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杂著
杂著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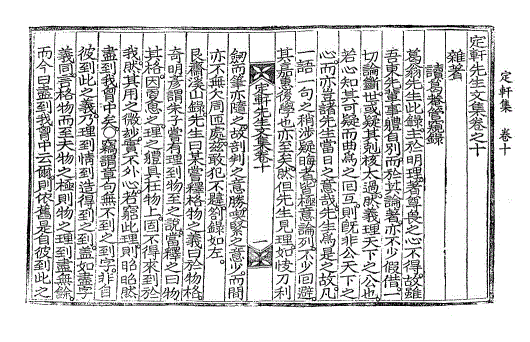 读葛庵管窥录
读葛庵管窥录葛翁先生此录。主于明理。著尊畏之心不得。故虽吾东先辈事体自别。而于其论著。亦不少假借。一切论断。世或疑其剋核太过。然义理天下之公也。若心知其可疑而曲为之回互。则既非公天下之心。而亦岂诸先生当日之意哉。先生为是之故。凡一语一句之稍涉疑晦者。皆极意论列。不少回避。其嘉惠后学也亦至矣。然但先生见理。如快刀利剑而笔亦随之。故剖判之意胜。吃紧之意少。而间亦不无欠周匝处。玆敢犯不韪。劄录如左。
艮斋溪山录。先生曰某尝释格物之义曰于物格。奇明彦谓朱子尝有理到物至之说。当释之曰物其格。因更思之。理之体具在物上。固不得来到于我。然其用之微妙。实不外心。若穷此理。则昭昭然尽到我胸中矣。○窃谓章句无不到之到字。非自彼到此之义。乃理到情到造得到之到。盖如尽字义同。言格物而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到尽无馀。而今曰尽到我胸中云尔。则依旧是自彼到此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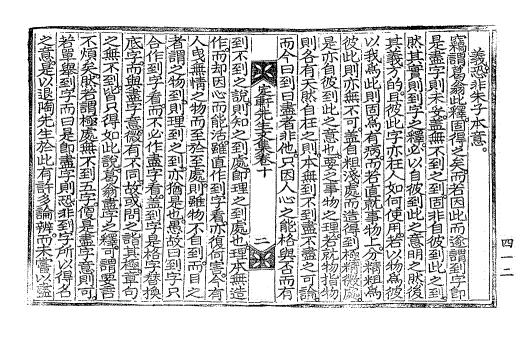 义。恐非朱子本意。
义。恐非朱子本意。窃谓葛翁此释。固得之矣。而若因此而遂谓到字即是尽字则未妥。盖无不到之到。固非自彼到此之到。然其实则到字之释。必以自彼到此之意明之然后其义方的。且彼此字亦在人如何使用。若以物为彼以我为此则固为有病。而若直就事物上。分精粗为彼此则亦无不可。盖自粗浅处而造得到极精微处。是亦自彼到此之意也。要之事物之理。若就物指物则各有天然自在之则。本无到不到尽不尽之可论。而今曰到曰尽者非他。只因人心之能格与否而有到不到之说。则知之到处。即理之到处也。理本无造作。而却因心而能活。虽直作到字看。亦复何害。今有人曳无情之物而至于至处。则虽物不自到。而目之者谓之物到。则理到之到。亦犹是也。愚故曰到字只合作到字看。而不必作尽字看。盖到字是格字替换底字。而与尽字意。微有不同。故或问之诣其极。章句之无不到。皆只得如此说。葛翁尽字之释。可谓要言不烦矣。然若谓极处无不到五字。便是尽字意则可。若单举到字而曰是即尽字则恐非到字所以得名之意。是以退陶先生于此有许多论辨。而未尝以尽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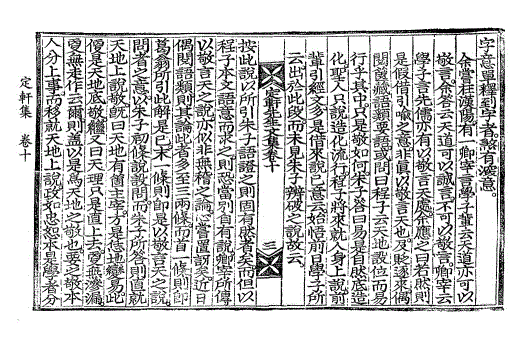 字意单释到字者。煞有深意。
字意单释到字者。煞有深意。余尝在汉阳。有一卿宰言学子辈云天道亦可以敬言。余答云天道可以诚言。不可以敬言。卿宰云学子言先儒亦有以敬言天处。余应之曰若然则是假借引喻之意。非真以敬言天也。及贬逐来。偶阅箧藏语类要语。或问曰程子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朱子答曰易是自然底造化。圣人只说造化流行。程子将来就人身上说。前辈引经文。多是借来说己意云。始悟前日学子所云。出于此段。而未见朱子辨破之说故云。
按此说以所引朱子语證之则固有然者矣。而但以程子本文语意而求之。则恐当别自有说。卿宰所传以敬言天之说。亦似非无稽之论。心尝置讶矣。近日偶阅语类。则其论此者多至三两条。而首一条则即葛翁所引此解是已。末一条则即是以敬言天之说。问者之意。以朱子初条说设问。而朱子所答则直就天地上说敬。既曰天地有个主宰。方是恁地变易。此便是天地底敬。继又曰天理只是直上去。更无渗漏。更无走作云尔。则盖以是为天地之敬也。要之敬本人分上事。而移就天地上说。政如忠恕本是学者分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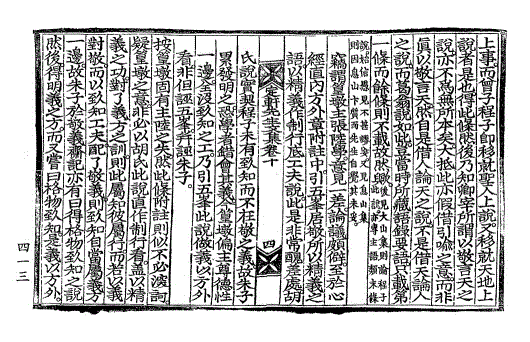 上事。而曾子程子即移就圣人上说。又移就天地上说者是也。得此条然后乃知卿宰所谓以敬言天之说。亦不为无所本矣。大抵此亦假借引喻之意。而非真以敬言天。然自是借人论天之说。不是借天论人之说。而葛翁说如此。岂当时所藏语录要语。只载第一条而馀条则不载故然欤。(后见大山集则论程子此说。亦专主语类末条说。始信愚见不甚谬妄。又见息山集则因息山卞质而先生自觉其未妥。)
上事。而曾子程子即移就圣人上说。又移就天地上说者是也。得此条然后乃知卿宰所谓以敬言天之说。亦不为无所本矣。大抵此亦假借引喻之意。而非真以敬言天。然自是借人论天之说。不是借天论人之说。而葛翁说如此。岂当时所藏语录要语。只载第一条而馀条则不载故然欤。(后见大山集则论程子此说。亦专主语类末条说。始信愚见不甚谬妄。又见息山集则因息山卞质而先生自觉其未妥。)窃谓篁墩主张陆学。意见一差。论议颇僻。至于心经直内方外章附注中。引五峰居敬所以精义之语。以精义作制行底工夫说。此是非常丑差处。胡氏说实契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义。故朱子累发明之。恐学者错会其义。今篁墩偏主尊德性一边。全没致知之工。乃引五峰此说做义以方外看。非但诬五峰。并诬朱子。
按篁墩固有主陆之失。然此条附注则似不必深诃。疑篁墩之意。非必以胡氏此说直作制行看。盖以精义之功。对了义方之训。则此属知彼属行。而若以义对敬。而以致知工夫。配了敬义。则致知自当属义方一边。故朱子于敬义斋记亦有曰得格物致知之说然后。得明义之方。而又尝曰格物致知。是义以方外。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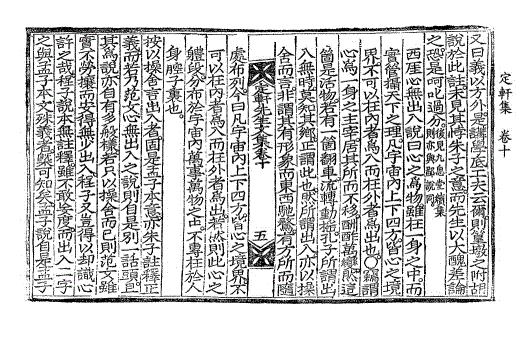 又曰义以方外。是讲学底工夫云尔。则篁墩之附胡说于此注。未见其悖朱子之意。而先生以大丑差论之。恐是呵叱过分。(后见九思堂续集则亦与鄙说同。)
又曰义以方外。是讲学底工夫云尔。则篁墩之附胡说于此注。未见其悖朱子之意。而先生以大丑差论之。恐是呵叱过分。(后见九思堂续集则亦与鄙说同。)西厓心无出入说曰心之为物。虽在一身之中。而实管摄天下之理。凡宇宙内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不可以在内者为入而在外者为出也。○窃谓心为一身之主宰。居其所而不移。酬酢万变。然这个是活物。若有一个翻车。流转动摇。孔子所谓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正谓此也。然所谓出入。亦以操舍而言。非谓其有形象而东西驰骛。有方所而随处布列。今曰凡宇宙内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不可以在内者为入而在外者为出。若然则此心之体段。分布于宇宙内万事万物之中。不专在于人身腔子里也。
按以操舍言出入者。固是孟子本意。亦朱子注释正义。而若乃范女心无出入之说则自是别一话头。且其为说。亦自有多般样。若只以操舍而已则范女虽实不劳攘而安得无少出入。程子又岂得以却识心许之哉。程子说本无注释。虽不敢妄度。而出入二字之与孟子本文殊义者。槩可知矣。孟子说自是孟子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4L 页
 说。程子说自是程子说。而厓翁此论。既以无出入做个题目。则所本者乃程子说也。非孟子说也。而葛翁乃以操舍出入之说槩之而斥其失。恐未妥当。且其驰骛布列之讥。亦似呵叱过分。西厓之言。本非训诂之谈。而自是抬起说阔大说。其曰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云者。特言心体至大。无不管摄而已。非有东西驰骛随处摆列之意。且既曰在一身之中而管摄天下之理。则心与物宾主之别。已自了然。心体自心体。上下四方自上下四方。则亦不必以分布宇宙之说。勒加把持。盖心之为物。本以应物。而贯动静该寂感。无远近无内外。本不可以出入言。程子所许范女之意。似出于此。故厓翁发明至此。而其曰不可以在内者为入而在外者为出云者。则实发挥出程子之意。恐不可歇后看。然亦非厓翁创立之说。朱子尝有心大无外固无出入之说。则厓翁此说。即心大无外之注脚也。又退陶先生引上蔡人心充满宇宙之说而答此句之问。则厓翁说不但追證于考亭。而亦溪门授受之旨也。要之厓翁以出入字本面论出入者。正所以发明操舍为出入之义也。心体上本无出入。故知得孟子所谓出入者。以操舍而言耳。葛翁乃反引
说。程子说自是程子说。而厓翁此论。既以无出入做个题目。则所本者乃程子说也。非孟子说也。而葛翁乃以操舍出入之说槩之而斥其失。恐未妥当。且其驰骛布列之讥。亦似呵叱过分。西厓之言。本非训诂之谈。而自是抬起说阔大说。其曰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云者。特言心体至大。无不管摄而已。非有东西驰骛随处摆列之意。且既曰在一身之中而管摄天下之理。则心与物宾主之别。已自了然。心体自心体。上下四方自上下四方。则亦不必以分布宇宙之说。勒加把持。盖心之为物。本以应物。而贯动静该寂感。无远近无内外。本不可以出入言。程子所许范女之意。似出于此。故厓翁发明至此。而其曰不可以在内者为入而在外者为出云者。则实发挥出程子之意。恐不可歇后看。然亦非厓翁创立之说。朱子尝有心大无外固无出入之说。则厓翁此说。即心大无外之注脚也。又退陶先生引上蔡人心充满宇宙之说而答此句之问。则厓翁说不但追證于考亭。而亦溪门授受之旨也。要之厓翁以出入字本面论出入者。正所以发明操舍为出入之义也。心体上本无出入。故知得孟子所谓出入者。以操舍而言耳。葛翁乃反引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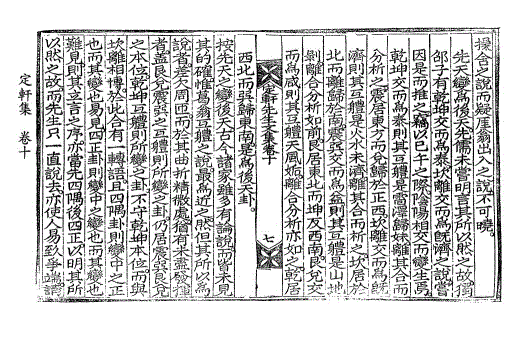 操舍之说而疑厓翁出入之说。不可晓。
操舍之说而疑厓翁出入之说。不可晓。先天变为后天。先儒未尝明言其所以然之故。独邵子有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之说。尝因是而推之。窃以巳午之际。阴阳相交而变生焉。乾坤交而为泰则其互体是䨓泽归妹。离其合而分析之。震居东方而兑归于正西。坎离交而为既济则其互体是火水未济。离其合而析之。坎居于北而离归于南。震巽交而为益则其互体是山地剥。离合分析如前。艮居东北而坤反西南。艮兑交而为咸则其互体天风姤。离合分析亦如之。乾居西北而巽归东南。是为后天卦。
按先天之变后天。古今诸家虽多有论说。而皆未见其的确。惟葛翁互体之说。最为近之。然但其所以为说者。差欠周匝。而于其曲折精微处。犹有未尽发挥者。盖艮兑震巽之互体则所变之卦。仍居震巽艮兑之本位。乾坤互体则所变之卦。不守乾坤本位。而与坎离相博。于此合有一转语。且四隅卦则变中之正也而其变也易见。四正卦则变中之变也而其变也难见。则其立言之序。亦当先四隅后四正。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而先生只一直说去。亦使人易致争端。请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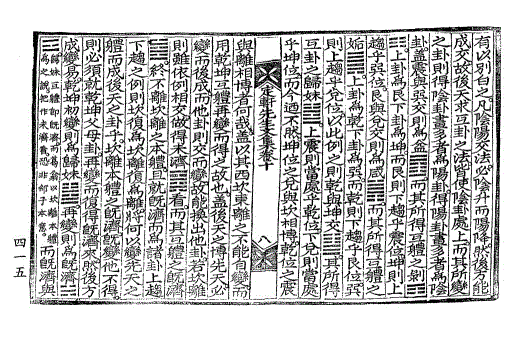 有以别白之。凡阴阳交法。必阴升而阳降。然后方能成交。故后天求互卦之法。皆使阴卦处上。而其所变之卦则得阴卦画多者为阳卦。得阳卦画多者为阴卦。盖震与巽交则为益䷩。而其所得互体之剥䷖。上卦为艮下卦为坤。而艮则下趋乎震位。坤则上趋乎巽位。艮与兑交则为咸䷞。而其所得互体之姤䷫。上卦为乾下卦为巽。而乾则下趋乎艮位。巽则上趋乎兑位。以此例之则乾与坤交䷊。其所得互卦之归妹䷵。上震则当处乎乾位。下兑则当处乎坤位。而今乃不然。坤位之兑与坎相博。乾位之震与离相博者何哉。盖以其西坎东离之不能自变。而用乾坤互体再变而得之故也。盖后天之博先天。必变而后成。而他卦则交而变。故能换出他卦。若坎离则虽依例相交。做得未济䷿看。而其互体之既济䷾。终不离坎离之本体。且就既济而为诸卦上趋下趋之例则坎复为坎离复为离。将何以变先天之体而成后天之卦乎。坎离本体之既济。既变他不得。则必须就乾坤父母卦。再变而复得既济来。然后方成变易。乾坤初变则为归妹䷵。再变则为既济䷾。(归妹互体即既济。而葛翁以坎离本体为之说。把作未济看。恐非邵子本意。)而既济与
有以别白之。凡阴阳交法。必阴升而阳降。然后方能成交。故后天求互卦之法。皆使阴卦处上。而其所变之卦则得阴卦画多者为阳卦。得阳卦画多者为阴卦。盖震与巽交则为益䷩。而其所得互体之剥䷖。上卦为艮下卦为坤。而艮则下趋乎震位。坤则上趋乎巽位。艮与兑交则为咸䷞。而其所得互体之姤䷫。上卦为乾下卦为巽。而乾则下趋乎艮位。巽则上趋乎兑位。以此例之则乾与坤交䷊。其所得互卦之归妹䷵。上震则当处乎乾位。下兑则当处乎坤位。而今乃不然。坤位之兑与坎相博。乾位之震与离相博者何哉。盖以其西坎东离之不能自变。而用乾坤互体再变而得之故也。盖后天之博先天。必变而后成。而他卦则交而变。故能换出他卦。若坎离则虽依例相交。做得未济䷿看。而其互体之既济䷾。终不离坎离之本体。且就既济而为诸卦上趋下趋之例则坎复为坎离复为离。将何以变先天之体而成后天之卦乎。坎离本体之既济。既变他不得。则必须就乾坤父母卦。再变而复得既济来。然后方成变易。乾坤初变则为归妹䷵。再变则为既济䷾。(归妹互体即既济。而葛翁以坎离本体为之说。把作未济看。恐非邵子本意。)而既济与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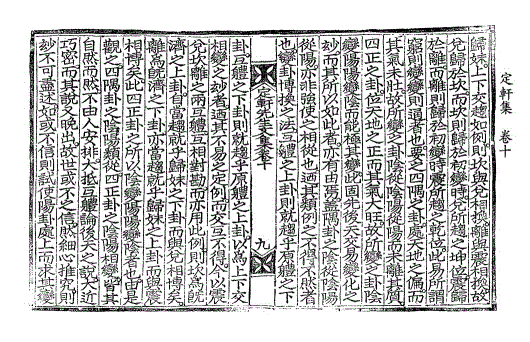 归妹。上下交趋如例。则坎与兑相换。离与震相换。故兑归于坎。而坎则归于初变时。兑所趋之坤位。震归于离。而离则归于初变时震所趋之乾位。此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者也。要之四隅之卦。处天地之偏。而其气未壮。故所变之卦阴从阴阳从阳而未离其质。四正之卦。位天地之正而其气大旺。故所变之卦阴变阳阳变阴而能极其变。此固先后天交易变化之妙。而其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焉。盖隅卦之阴从阴阳从阳。亦非强使之相从也。乃其类例之不得不然者也。变卦博换之法。互体之上卦则就趋乎原体之下卦。互体之下卦则就趋乎原体之上卦。以为上下交相变之妙者。乃其不易之定例。而交互不得。今以震兑坎离之两互体。互相对勘。而亦用此例。则坎为既济之上卦。自当趋就乎归妹之下卦而与兑相博矣。离为既济之下卦。亦当趋就乎归妹之上卦而与震相博矣。此四正卦之所以阴变阳阳变阴者也。由是观之。四隅卦之阴阳类从。四正卦之阴阳相变。皆其自然而然。不由人安排。大抵互体论后天之说。大近巧密。而其说又晚出。故世或不之信。然细心推究。则妙不可尽述。如或不信则试使阳卦处上而求其变
归妹。上下交趋如例。则坎与兑相换。离与震相换。故兑归于坎。而坎则归于初变时。兑所趋之坤位。震归于离。而离则归于初变时震所趋之乾位。此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者也。要之四隅之卦。处天地之偏。而其气未壮。故所变之卦阴从阴阳从阳而未离其质。四正之卦。位天地之正而其气大旺。故所变之卦阴变阳阳变阴而能极其变。此固先后天交易变化之妙。而其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焉。盖隅卦之阴从阴阳从阳。亦非强使之相从也。乃其类例之不得不然者也。变卦博换之法。互体之上卦则就趋乎原体之下卦。互体之下卦则就趋乎原体之上卦。以为上下交相变之妙者。乃其不易之定例。而交互不得。今以震兑坎离之两互体。互相对勘。而亦用此例。则坎为既济之上卦。自当趋就乎归妹之下卦而与兑相博矣。离为既济之下卦。亦当趋就乎归妹之上卦而与震相博矣。此四正卦之所以阴变阳阳变阴者也。由是观之。四隅卦之阴阳类从。四正卦之阴阳相变。皆其自然而然。不由人安排。大抵互体论后天之说。大近巧密。而其说又晚出。故世或不之信。然细心推究。则妙不可尽述。如或不信则试使阳卦处上而求其变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6L 页
 卦观其互体。则一一皆后天之正配而不相溷淆。是岂偶然而然乎。少时读易。偶自推测到此。而不敢自信。得先生说然后。始窃自幸谬妄之见。偶合于先生之论。而但先生既以互体论此。则隅正之同异。乾坤之变易。必须抉摘而阐明之然后。方不致人疑。而却不之及。岂只欲微启其端而使人自致思者欤。○按乾坤再变。亦缘本卦有可变之理。故变得如此。若艮兑震巽之交则虽欲再变而有不可得。盖艮兑再变则其互体为纯乾而犯了初变之上卦。震巽再变则其互体为纯坤而亦犯初变之下卦。惟乾坤然后方成再变。而乾坤自具坎离之体。亦异矣哉。康节所谓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者。味其语势。似是为此而发。如此然后乾坤之变坎离。坎离之变震兑。皆有例可推。若只如葛翁说而已。则坎离之宅乾坤。震兑之处坎离。发之无端。而与隅卦之例不合。故僭因邵子说而推究得如此为乾坤再变之法。观者勿遽以穿凿病之。而留心看取也哉。
卦观其互体。则一一皆后天之正配而不相溷淆。是岂偶然而然乎。少时读易。偶自推测到此。而不敢自信。得先生说然后。始窃自幸谬妄之见。偶合于先生之论。而但先生既以互体论此。则隅正之同异。乾坤之变易。必须抉摘而阐明之然后。方不致人疑。而却不之及。岂只欲微启其端而使人自致思者欤。○按乾坤再变。亦缘本卦有可变之理。故变得如此。若艮兑震巽之交则虽欲再变而有不可得。盖艮兑再变则其互体为纯乾而犯了初变之上卦。震巽再变则其互体为纯坤而亦犯初变之下卦。惟乾坤然后方成再变。而乾坤自具坎离之体。亦异矣哉。康节所谓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者。味其语势。似是为此而发。如此然后乾坤之变坎离。坎离之变震兑。皆有例可推。若只如葛翁说而已。则坎离之宅乾坤。震兑之处坎离。发之无端。而与隅卦之例不合。故僭因邵子说而推究得如此为乾坤再变之法。观者勿遽以穿凿病之。而留心看取也哉。历家日法度分。皆用九百四十分。至许鲁斋乃以万分为率。似差简略。然十九分度之七。犹有零欠不齐之弊。朱子尝有历法当用季通说之语。愚尝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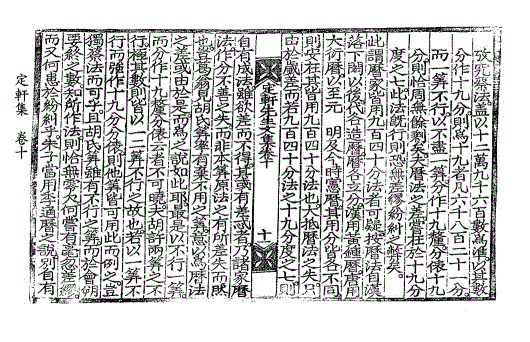 考究蔡法。盖以十二万九千六百数为准。以其数分作十九分。则为十九者凡六千八百二十一分。而一算不行。以不尽一算。分作十九釐。分俵十九分。则恰周无馀剩矣。夫历法之差。尝在于十九分度之七。此法既行则恐无差缪纷纠之弊矣。
考究蔡法。盖以十二万九千六百数为准。以其数分作十九分。则为十九者凡六千八百二十一分。而一算不行。以不尽一算。分作十九釐。分俵十九分。则恰周无馀剩矣。夫历法之差。尝在于十九分度之七。此法既行则恐无差缪纷纠之弊矣。此谓历家皆用九百四十分法者可疑。按历法自汉落下闳以后。代各造历。历各立分。汉用黄钟历。唐用大衍历。以至元 明及今时宪历。其用分皆各不同。则安在其皆用九百四十分法也。大抵历法之失。只由于岁差。而若九百四十分法之十九分度之七。则自有成法。虽欲差而不得。其或有差忒者。乃诸家历法。作分不善之失。而非本算原法之有所差失而然也。岂葛翁见胡氏算率有弃不用之算。意以为历法之差或由于是。而为之说如此耶。最是以不行一算。而分作十九釐分俵云者不可晓。夫胡许两算之不行。极其数则皆以一二算不行之故也。若以一算不行而强作十九分分俵。则他算皆可用此而例之。岂独蔡法而可乎。且胡氏算虽有不行之算。而于会朔要终之数。知所作法。则恰无零欠。何尝有毫忽差缪。而又何患于纷纠乎。朱子当用季通历之说。别自有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4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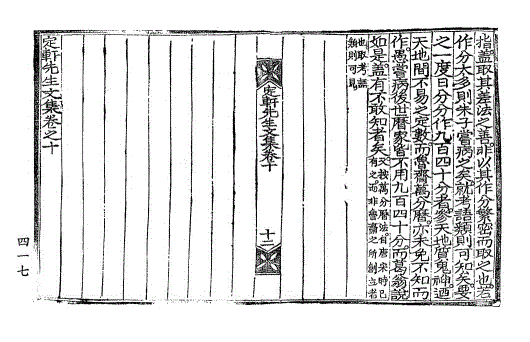 指。盖取其差法之善。非以其作分繁密而取之也。若作分太多则朱子尝病之矣。就考语类则可知矣。要之一度日分分作九百四十分者。参天地质鬼神。乃天地间不易之定数。而鲁斋万分历。亦未免不知而作。愚尝病后世历家皆不用九百四十分。而葛翁说如是。盖有不敢知者矣。(又按万分历法。自唐宋时已有之。而非鲁斋之所创立者也。取考语类则可见。)
指。盖取其差法之善。非以其作分繁密而取之也。若作分太多则朱子尝病之矣。就考语类则可知矣。要之一度日分分作九百四十分者。参天地质鬼神。乃天地间不易之定数。而鲁斋万分历。亦未免不知而作。愚尝病后世历家皆不用九百四十分。而葛翁说如是。盖有不敢知者矣。(又按万分历法。自唐宋时已有之。而非鲁斋之所创立者也。取考语类则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