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x 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杂著
杂著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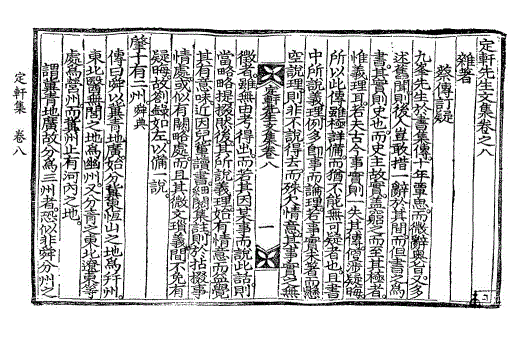 蔡传订疑
蔡传订疑九峰先生于书集传。十年覃思。而微辞奥旨。又多述旧闻。则后人岂敢措一辞于其间。而但书之为书。其实则史也。而史主故实。盖穷之而至其极者。惟义理耳。若夫古今事实则一失其传。便涉疑晦。所以此传虽极详备。而犹不能无可疑者也。且书中所说义理。例多即事而论理。若事实未著而悬空说理。则非不说得去。而殊欠情意。其事实之无徵者。虽无由考得出。而若其因某事而说此话。则当略略提掇然后。其所说义理。始有情意而益觉其有意味。近因儿辈读书。细阅集注。则于拈掇事情处。或似有阙略处。而且其微文琐义。间不免有疑晦。故劄录如左。以备一说。
肇十有二州。(舜典)
传曰舜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
谓冀青地广故分为三州者。恐似非舜分州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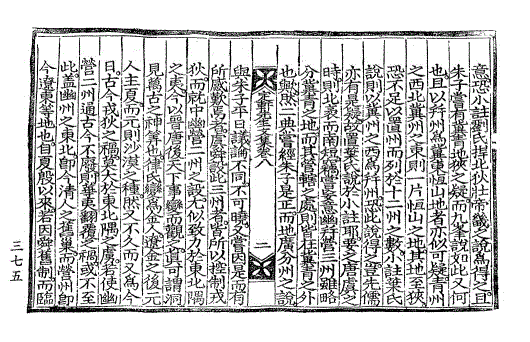 意。恐小注刘氏捍北狄壮帝畿之说为得之。且朱子尝有冀青地狭之疑。而九峰说如此又何也。且以并州为冀东恒山地者亦似可疑。青州之西北冀州之东则一片恒山之地。其地至狭。恐不足以置州而列于十二州之数。小注叶氏说则以冀州之西为并州。恐此说得之。岂先儒亦有是疑。故置叶氏说于小注耶。要之唐虞之时。则北袤而南短。窃尝妄意幽并营三州虽略分冀青之地。而其管辖之处则皆在冀青之外也欤。然二典尝经朱子是正。而地广分州之说。与朱子平日议论不同。不可晓。又尝因是而有所感叹焉者。虞舜设此三州者。皆所以控制戎狄。而就中幽营二州之设。尤似致力于东北隅之夷。今以晋唐后天下事变而观之。真可谓洞见万古之神算也。律氏变为金人。辽金之后元人主夏。而元则沙漠之种。然又不久而又为今日。古今戎狄之祸。莫大于东北隅之虏。若使幽营二州通古今不废。则华夷翻覆之祸。或不至此。盖幽州之东北。即今清人之旧巢。而营州即今辽东等地也。自夏殷以来。若因舜旧制。而临
意。恐小注刘氏捍北狄壮帝畿之说为得之。且朱子尝有冀青地狭之疑。而九峰说如此又何也。且以并州为冀东恒山地者亦似可疑。青州之西北冀州之东则一片恒山之地。其地至狭。恐不足以置州而列于十二州之数。小注叶氏说则以冀州之西为并州。恐此说得之。岂先儒亦有是疑。故置叶氏说于小注耶。要之唐虞之时。则北袤而南短。窃尝妄意幽并营三州虽略分冀青之地。而其管辖之处则皆在冀青之外也欤。然二典尝经朱子是正。而地广分州之说。与朱子平日议论不同。不可晓。又尝因是而有所感叹焉者。虞舜设此三州者。皆所以控制戎狄。而就中幽营二州之设。尤似致力于东北隅之夷。今以晋唐后天下事变而观之。真可谓洞见万古之神算也。律氏变为金人。辽金之后元人主夏。而元则沙漠之种。然又不久而又为今日。古今戎狄之祸。莫大于东北隅之虏。若使幽营二州通古今不废。则华夷翻覆之祸。或不至此。盖幽州之东北。即今清人之旧巢。而营州即今辽东等地也。自夏殷以来。若因舜旧制。而临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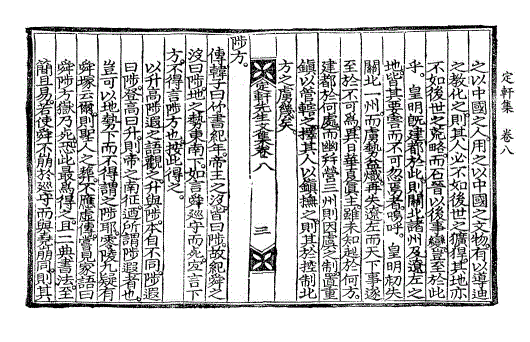 之以中国之人。用之以中国之文物。有以导迪之教化之。则其人必不如后世之犷悍。其地亦不如后世之荒略。而石晋以后事变。岂至于此乎。 皇明既建都于此。则关北诸州及辽左之地。皆其要害而不可忽焉者。呜呼。 皇明初失关北一州。而虏势益炽。再失辽左而天下事遂至于不可为。异日华夏真主。虽未知起于何方。建都于何处。而幽并营三州则因虞之制。置重镇以管辖之。择其人以镇抚之。则其于控制北方之虏几矣。
之以中国之人。用之以中国之文物。有以导迪之教化之。则其人必不如后世之犷悍。其地亦不如后世之荒略。而石晋以后事变。岂至于此乎。 皇明既建都于此。则关北诸州及辽左之地。皆其要害而不可忽焉者。呜呼。 皇明初失关北一州。而虏势益炽。再失辽左而天下事遂至于不可为。异日华夏真主。虽未知起于何方。建都于何处。而幽并营三州则因虞之制。置重镇以管辖之。择其人以镇抚之。则其于控制北方之虏几矣。陟方。
传韩子曰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故纪舜之没曰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
以升高陟遐之语观之。升与陟。本自不同。陟遐曰陟。登高曰升。则帝之南征。乃所谓陟遐者也。岂可以地势下而不得谓之陟耶。零陵九疑有舜冢云尔。则圣人之葬。不应虚传。尝见家语曰舜陟方岳乃死。恐此最为得之。且二典书法。至简且易。若使舜不崩于巡守而与尧崩同。则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6L 页
 书法自当依尧崩书殂落。岂容别立书法如此耶。竹书之书没曰陟。自是伪书者。窃取陟方礼陟等语。以文其说。恐不当以彼而證此。与其引汲书以證之。又岂若證引家语之犹为近雅乎。家语虽非纯书。而此等古实则当必有所受矣。但典谟既经朱子是正。则当必有说。虽不敢妄为之说。而有疑于心。不敢强焉。故私记之如此。(按见行家语板本。方字之下。或有岳字。或无岳字。)
书法自当依尧崩书殂落。岂容别立书法如此耶。竹书之书没曰陟。自是伪书者。窃取陟方礼陟等语。以文其说。恐不当以彼而證此。与其引汲书以證之。又岂若證引家语之犹为近雅乎。家语虽非纯书。而此等古实则当必有所受矣。但典谟既经朱子是正。则当必有说。虽不敢妄为之说。而有疑于心。不敢强焉。故私记之如此。(按见行家语板本。方字之下。或有岳字。或无岳字。)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益稷)
传禹因孜孜之义。述其治水本末先后之详。而警戒之意。实存于其间。
按传虽曰警戒之意存于其中。然若以懋迁以下。皆看作已然说。则终是自叙治绩之意胜。窃尝妄疑奏庶艰鲜以上。乃禹自述治水奠民之绩。而懋迁有无以下则恐是当时急务。其意若曰洪水滔天。民之昏垫如此。吾虽竭力治水。暨稷耕播。而天下尚艰食。又犹有鲜食处。必须懋迁有无。化其居积然后。烝民乃皆粒而万邦作乂云尔。要之水害虽甫去。而以禹贡考之。犹有作十有三载乃同之文。则四海九州之大。犹有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7H 页
 艰食之处可知。若已耕治之处。则九年抛荒之馀。其收当倍。泄其有馀之谷而济其艰食之民。岂非治水后急先务乎。盖禹之先叙己绩。乃为此而设。非徒然而发。政如下段将欲言苗顽不即工。故先叙荒度土功及各迪有功之语耳。且万邦作乂之云。自是极致之语。虽邃古言语。不避嫌碍。而不应以此自居。若如传说。则皋陶应俞之辞。亦当曰嘉乃丕绩。而不应曰师汝昌言。
艰食之处可知。若已耕治之处。则九年抛荒之馀。其收当倍。泄其有馀之谷而济其艰食之民。岂非治水后急先务乎。盖禹之先叙己绩。乃为此而设。非徒然而发。政如下段将欲言苗顽不即工。故先叙荒度土功及各迪有功之语耳。且万邦作乂之云。自是极致之语。虽邃古言语。不避嫌碍。而不应以此自居。若如传说。则皋陶应俞之辞。亦当曰嘉乃丕绩。而不应曰师汝昌言。禹曰俞哉。(止。)万邦黎献。共惟帝臣。
传曰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
窃意禹之于帝。不尽然其言者。非以其专尚威刑也。且以上文观之。其曰格庸否威者。不但惩恶而已。格之庸之而不得已而后威之。则帝之意。岂专在于加之以威而已哉。特帝则方求助于臣邻。故其激劝之意。只止于在庭之臣僚。禹则欲其广招贤俊。故其加勉之意。乃在于万邦之黎献。盖禹之意。若曰帝于见在之臣僚。惩顽劝善。惓惓至此者。固无不可。而但天下之贤才未及登庸者至多。不必取足于在庭之臣僚而止耳。当延四方之黎献。试其功庸云尔。然则禹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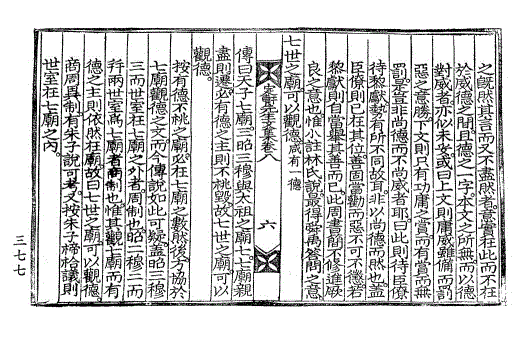 之既然其言而又不尽然者。意实在此而不在于威德之间。且德之一字。本文之所无。而以德对威者。亦似未妥。或曰上文则庸威虽备而罚恶之意胜。下文则只有功庸之赏。而有赏而无罚。是岂非尚德而不尚威者耶。曰此则待臣僚待黎献。势有所不同故耳。非以尚德而然也。盖臣僚则已在其位。善固当劝而恶不可不惩。若黎献则自当举其善而已。此周书简不修进厥良之意也。惟小注林氏说。最得舜禹答问之意。
之既然其言而又不尽然者。意实在此而不在于威德之间。且德之一字。本文之所无。而以德对威者。亦似未妥。或曰上文则庸威虽备而罚恶之意胜。下文则只有功庸之赏。而有赏而无罚。是岂非尚德而不尚威者耶。曰此则待臣僚待黎献。势有所不同故耳。非以尚德而然也。盖臣僚则已在其位。善固当劝而恶不可不惩。若黎献则自当举其善而已。此周书简不修进厥良之意也。惟小注林氏说。最得舜禹答问之意。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咸有一德)
传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七庙亲尽则迁。必有德之主则不祧毁。故七世之庙。可以观德。
按有德不祧之庙。必在七庙之数然后。方协于七庙观德之文。而今传说如此可疑。盖昭三穆三而世室在七庙之外者。周制也。昭二穆二而并两世室为七庙者商制也。惟其观七庙而有德之主则依然在庙。故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商周异制。有朱子说可考。又按朱子禘祫议则世室在七庙之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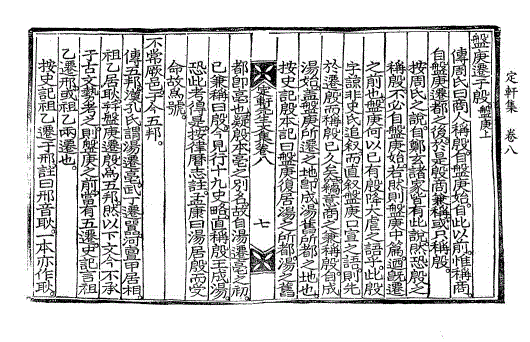 盘庚迁于殷。(盘庚上)
盘庚迁于殷。(盘庚上)传周氏曰商人称殷。自盘庚始。自此以前。惟称商。自盘庚迁都之后。于是殷商兼称。或只称殷。
按周氏之说。自郑玄诸家皆有此说。然恐殷之称殷。不必自盘庚始。若然则盘庚中篇。乃既迁之前也。盘庚何以已有殷降大虐之语乎。此殷字谅非史氏追叙。而直叙盘庚口宣之语。则先于迁殷而称殷已久矣。窃意商之兼称殷。自成汤始。盖盘庚所迁之地。即成汤旧所都之地也。按史记殷本记曰盘庚复居汤之所都。汤之旧都即亳也。疑殷本亳之别名。故自汤迁亳之初。已兼称曰殷。今见行十九史略。直称殷王成汤。恐此考得是。按律历志注。孟康曰汤居殷而受命故为号。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传五邦。汉孔氏谓汤迁亳。武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盘庚迁殷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势考之。则盘庚之前。当有五迁。史记言祖乙迁邢。或祖乙两迁也。
按史记祖乙迁于邢。注曰邢音耿。一本亦作耿。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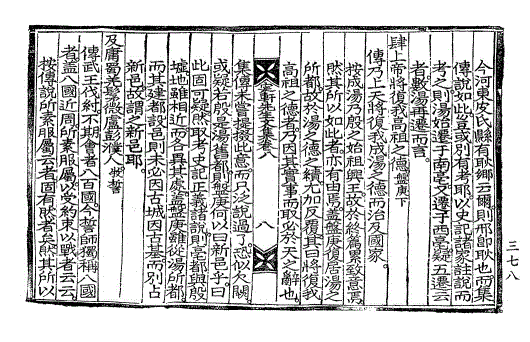 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云尔。则邢即耿也。而集传说如此。岂或别有考耶。以史记诸家注说而考之。则汤始迁于南亳。又迁于西亳。疑五迁云者。数汤再迁而言。
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云尔。则邢即耿也。而集传说如此。岂或别有考耶。以史记诸家注说而考之。则汤始迁于南亳。又迁于西亳。疑五迁云者。数汤再迁而言。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盘庚下)
传乃上天将复我成汤之德而治及国家。
按成汤乃殷之始祖兴王。故于终篇累致意焉。然其所以如此者。亦有由焉。盖盘庚复居汤之所都。故于汤之德之绩。尤加反覆。其曰将复我高祖之德者。乃因其实事而取必于天之辞也。集传未尝提掇此意。而只泛说过了。恐似欠阙。或疑若殷是汤旧都。则盘庚何以曰新邑乎。曰此固可疑。然取考史记正义诸说。则亳都与殷墟。地虽相近。而各异其处。盖盘庚虽从汤所都。而其建都设邑则未必因古城因古基。而别占新邑。故谓之新邑耶。
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牧誓)
传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所素服属。以受约束以战者云云。
按传说所素服属云者。固有然者矣。然其所以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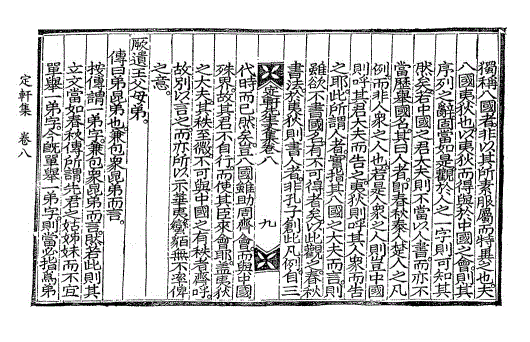 独称八国者。非以其所素服属而特异之也。夫八国夷狄也。以夷狄而得与于中国之会。则其序列之辞。固当如是。观于人之一字则可知其然矣。若中国之君大夫则不当以人书。而亦不当历举国名。其曰人者。即春秋秦人楚人之凡例。而非人众之人也。若是人众之人则岂中国则呼其君大夫而告之。夷狄则呼其人众而告之耶。此所谓人者。实指其八国之大夫而言。则虽欲不书国名。有不可得者矣。以此观之。春秋书法。于夷狄则书人者。非孔子创此凡例。自三代时而已然矣。岂八国虽助周齐会。而与中国殊界。故其君不自行。而使其臣来会耶。盖夷狄之大夫。其秩至微。不可与中国之有秩者齐呼。故别以言之。而亦所以示华夷蛮貊无不率俾之意。
独称八国者。非以其所素服属而特异之也。夫八国夷狄也。以夷狄而得与于中国之会。则其序列之辞。固当如是。观于人之一字则可知其然矣。若中国之君大夫则不当以人书。而亦不当历举国名。其曰人者。即春秋秦人楚人之凡例。而非人众之人也。若是人众之人则岂中国则呼其君大夫而告之。夷狄则呼其人众而告之耶。此所谓人者。实指其八国之大夫而言。则虽欲不书国名。有不可得者矣。以此观之。春秋书法。于夷狄则书人者。非孔子创此凡例。自三代时而已然矣。岂八国虽助周齐会。而与中国殊界。故其君不自行。而使其臣来会耶。盖夷狄之大夫。其秩至微。不可与中国之有秩者齐呼。故别以言之。而亦所以示华夷蛮貊无不率俾之意。厥遗王父母弟。
传曰弟昆弟也。兼包众昆弟而言。
按传谓一弟字。兼包众昆弟而言。然若此则其立文当如春秋传所谓先君之姑姊妹而不宜单举一弟字。今既单举一弟字。则当必指为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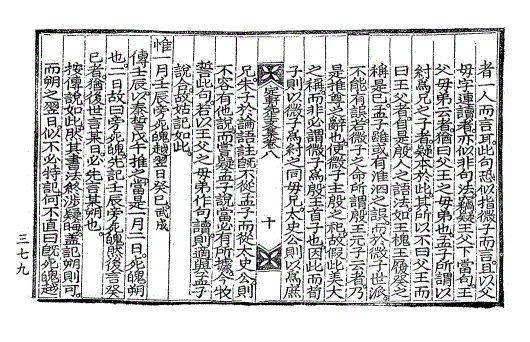 者一人而言耳。此句恐似指微子而言。且以父母字连读者。亦似非句法。窃疑王父下当句。王父母弟云者。犹曰父王之母弟也。孟子所谓以纣为兄之子者。疑本于此。其所以不曰父王而曰王父者。自是殷人之语法。如王槐王履癸之称是已。孟子虽或有淮泗之误。而于微子世派。不能有误。若微子之命所谓殷王元子云者。乃是推尊之辞也。使微子主殷之祀。故假此美大之称。而非必谓微子为殷王首子也。因此而荀子则以微子为纣之同母兄。太史公则以为庶兄。朱子于论语注既不从孟子而从太史公。则不容有他说。而尝疑孟子说当必有所据。今牧誓此句。若以王父之母弟作句读。则适与孟子说合。故姑记如此。
者一人而言耳。此句恐似指微子而言。且以父母字连读者。亦似非句法。窃疑王父下当句。王父母弟云者。犹曰父王之母弟也。孟子所谓以纣为兄之子者。疑本于此。其所以不曰父王而曰王父者。自是殷人之语法。如王槐王履癸之称是已。孟子虽或有淮泗之误。而于微子世派。不能有误。若微子之命所谓殷王元子云者。乃是推尊之辞也。使微子主殷之祀。故假此美大之称。而非必谓微子为殷王首子也。因此而荀子则以微子为纣之同母兄。太史公则以为庶兄。朱子于论语注既不从孟子而从太史公。则不容有他说。而尝疑孟子说当必有所据。今牧誓此句。若以王父之母弟作句读。则适与孟子说合。故姑记如此。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武成)
传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当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先记壬辰旁死魄然后言癸巳者。犹后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
按传说如此。然其书法终涉疑晦。盖记朔则可。而朔之翌日。似不必特记。何不直曰既死魄越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0H 页
 二日癸巳。而必以旁死魄之次日立文乎。此是可疑之大者也。或曰旁死魄即朔日也。癸巳乃朔后次日。故先记朔而次记日。其曰旁死魄云者。疑月之魄死明生。从一旁而起。故谓之旁死魄。旁是月旁之旁。非次日之旁。是以经文四月之既生魄。汉书律历志则作旁生魄。以此观之。班氏亦以既生魄与旁生魄。作同日看者审矣。此说似有理。然又取考律历志则周之元年正月朔日为辛卯云。而以诗所谓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之语参考。则周之元年正月朔日为辛卯云者。似不为无證。盖周家元年初朔在辛卯。故辛卯日食。周人最忌之。则九峰之以壬辰旁死魄为初二日者。其果有据矣。然其必以初二日旁死魄记朔者。当必有说。朱子曰前月大尽则初二日生明。前月小尽则初三日生明云。尝以是说而验之于月体则二日生明之月。死魄之意在一日。三日生明之月则死魄之意在二日。岂古者记朔之法。随月大小而大尽馀记朔则以正死魄记朔。小尽馀记朔则以旁死魄记朔故然欤。
二日癸巳。而必以旁死魄之次日立文乎。此是可疑之大者也。或曰旁死魄即朔日也。癸巳乃朔后次日。故先记朔而次记日。其曰旁死魄云者。疑月之魄死明生。从一旁而起。故谓之旁死魄。旁是月旁之旁。非次日之旁。是以经文四月之既生魄。汉书律历志则作旁生魄。以此观之。班氏亦以既生魄与旁生魄。作同日看者审矣。此说似有理。然又取考律历志则周之元年正月朔日为辛卯云。而以诗所谓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之语参考。则周之元年正月朔日为辛卯云者。似不为无證。盖周家元年初朔在辛卯。故辛卯日食。周人最忌之。则九峰之以壬辰旁死魄为初二日者。其果有据矣。然其必以初二日旁死魄记朔者。当必有说。朱子曰前月大尽则初二日生明。前月小尽则初三日生明云。尝以是说而验之于月体则二日生明之月。死魄之意在一日。三日生明之月则死魄之意在二日。岂古者记朔之法。随月大小而大尽馀记朔则以正死魄记朔。小尽馀记朔则以旁死魄记朔故然欤。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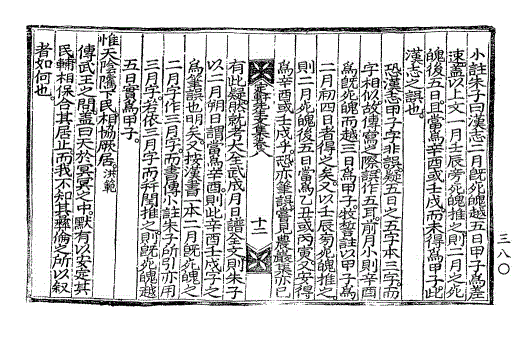 小注朱子曰汉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为差速。盖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则二月之死魄后五日。且当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为甲子。此汉志之误也。
小注朱子曰汉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为差速。盖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则二月之死魄后五日。且当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为甲子。此汉志之误也。恐汉志甲子字非误。疑五日之五字本三字。而字相似。故传写之际。误作五耳。前月小则辛酉为既死魄而越三日为甲子。牧誓注以甲子为二月初四日者得之矣。又以壬辰旁死魄推之。则二月死魄后五日当为乙丑或丙寅。又安得为辛酉或壬戌乎。恐亦笔误。尝见农岩集亦已有此疑。然就考大全武成月日谱全文。则朱子以二月朔日谓当为辛酉。则此辛酉壬戌字之为笔误也明矣。又按汉书一本二月既死魄之二月字作三月字。而书传小注朱子所引亦用三月字。若依三月字而并闰推之。则既死魄越五日实为甲子。
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洪范)
传武王之问。盖曰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辅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伦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1H 页
 谨按 太祖高皇帝。以蔡氏此注为未协。而改注以颁天下。盖 圣祖之意。以为辅相和协。以奠民居者。实人君之事。而专归之天者。为未尽故也。然人君之所以能使民底定者。实奉行天意。则蔡氏之说未见其不可。而睿意如此。虽不敢妄度。然其以此释为未惬者。则实卓越千古之见。窃尝妄谓武王访问之初。首发此句语者。非泛论天道也。乃所以自述其革命安民之事。而箕子殷人也。对箕子而不敢直致其辞。故假天意以明之耳。如文侯之命。言幽王之殄绝而不敢斥言。但曰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者是已。又如左传吕相所对晋人一句语。皆是此等语法。九峰于此未尝提掇此意。而只沿文释义而止。此所以起 高皇帝之疑也。武王之意。若曰吾虽恭行天罚。奠安民居。而陈教则未也。故为此访问云尔。然则这一句。乃所以自道也。然不敢自居而归之于天者。对箕子之辞。不得不然耳。惜乎九峰之欠此一转语也。
谨按 太祖高皇帝。以蔡氏此注为未协。而改注以颁天下。盖 圣祖之意。以为辅相和协。以奠民居者。实人君之事。而专归之天者。为未尽故也。然人君之所以能使民底定者。实奉行天意。则蔡氏之说未见其不可。而睿意如此。虽不敢妄度。然其以此释为未惬者。则实卓越千古之见。窃尝妄谓武王访问之初。首发此句语者。非泛论天道也。乃所以自述其革命安民之事。而箕子殷人也。对箕子而不敢直致其辞。故假天意以明之耳。如文侯之命。言幽王之殄绝而不敢斥言。但曰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下民者是已。又如左传吕相所对晋人一句语。皆是此等语法。九峰于此未尝提掇此意。而只沿文释义而止。此所以起 高皇帝之疑也。武王之意。若曰吾虽恭行天罚。奠安民居。而陈教则未也。故为此访问云尔。然则这一句。乃所以自道也。然不敢自居而归之于天者。对箕子之辞。不得不然耳。惜乎九峰之欠此一转语也。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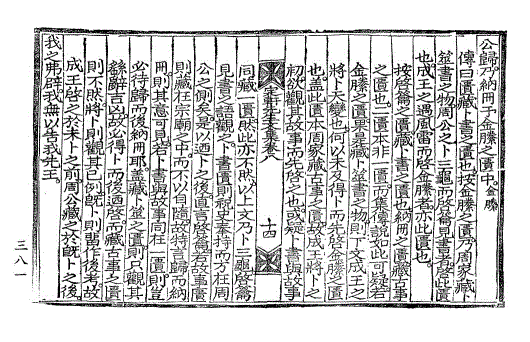 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金縢)
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金縢)传曰匮藏卜书之匮也。按金縢之匮。乃周家藏卜筮书之物。周公之卜三龟而启籥见书者。启此匮也。成王之遇风雷而启金縢者。亦此匮也。
按启籥之匮。藏卜书之匮也。纳册之匮。藏古事之匮也。二匮本非一匮。而集传说如此可疑。若金縢之匮。果是藏卜筮书之物。则下文成王之将卜天变也。何以未及得卜而先启金縢之匮也。盖此匮本周家藏古事之匮。故成王将卜之初。欲观其故事而先启之也。或疑卜书与故事同藏一匮。然此亦不然。以上文乃卜三龟。启籥见书之语观之。卜书匮则祝史奉持而方在周公之侧矣。是以乃卜之后。直言启籥。若故事匮则藏在宗庙之中。而不以自随。故特言归而纳册。则其意可见。若卜书与故事同在一圚。则岂必待归而后纳册耶。盖藏卜筮之匮。则只观其繇辞吉凶。故必得卜而后乃启。而藏古事之匮则不然。将卜则观其已例。既卜则留作后考。故成王启之于未卜之前。周公藏之于既卜之后。
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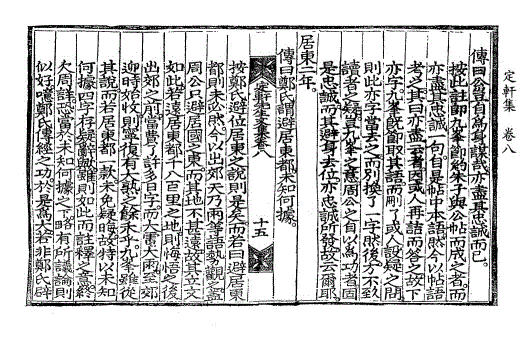 传曰公岂自为身谋哉。亦尽其忠诚而已。
传曰公岂自为身谋哉。亦尽其忠诚而已。按此注即九峰节约朱子与公帖而成之者。而亦尽其忠诚一句。自是帖中本语。然今以帖语考之。其曰亦尽云者。因或人再诘而答之。故下亦字。九峰既节取其语。而删了或人设疑之问。则此亦字当去之。而别换了一字然后。方不致读者之疑。岂九峰之意。周公之自以为功者。固是忠诚。而其避身去位。亦忠诚所发。故云尔耶。
居东二年。
传曰郑氏谓避居东都。未知何据。
按郑氏避位居东之说则是矣。而若曰避居东都则未必然。今以出郊天乃雨等语势观之。盖周公只避居国之东。而其地不甚远。故其立文如此。若远居东都千八百里之地。则悔悟之后出郊之前。当费了许多日字。而大电大雨。至郊迎时始收。则宁复有大熟之馀禾乎。九峰虽从其说。而若居东都一款。未免疑晦。故特以未知何据四字存疑辞欤。虽则如此而注释之意。终欠周详。恐当于未知何据之下。略有所议论则似好。噫郑氏传经之功。于是为大。若非郑氏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2L 页
 位居东一说。则周公之心与事。终无以著白于天下万世矣。要之周公一身。虽系天下安危。而当初流言则事系一身。不得不辟位息言。及东辙既西。彼与武庚叛则事关王室。而呼吸之间。安危立办。不得不兴兵诛讨。周公始终如是而已。曷尝有以弟杀兄之事。东征之举。非周公得已而不已也。彼既称兵至此。则周公虽欲不诛。亦有不可得者矣。朱子所谓周公东征。不必言用权者此也。窃尝谓自古圣人。虽或身遭不幸。而不幸之甚。未有如周公者。舜之处顽嚚傲弟之间者。虽甚不幸。而天下之为父子兄弟者由是而定。是舜之不幸而实天下万世之幸也。若周公则其身既不幸矣。而因事实之讹谬。遂为天下万世之大不幸。以复辟为践阼而王莽借之。几移汉鼎。以居东为东征而唐太宗假之。蹀血禁门。呜呼。使管蔡止于流言而已。则其心不过倾周公之位而夺周公之权而已。周公岂肯容心于其间哉。苟得毋毁王室则幸矣。苟得保全成王则幸矣。此鸱鸮诗之意也。假使成王终不悟。亦不过优游东郊。安得天分而已。
位居东一说。则周公之心与事。终无以著白于天下万世矣。要之周公一身。虽系天下安危。而当初流言则事系一身。不得不辟位息言。及东辙既西。彼与武庚叛则事关王室。而呼吸之间。安危立办。不得不兴兵诛讨。周公始终如是而已。曷尝有以弟杀兄之事。东征之举。非周公得已而不已也。彼既称兵至此。则周公虽欲不诛。亦有不可得者矣。朱子所谓周公东征。不必言用权者此也。窃尝谓自古圣人。虽或身遭不幸。而不幸之甚。未有如周公者。舜之处顽嚚傲弟之间者。虽甚不幸。而天下之为父子兄弟者由是而定。是舜之不幸而实天下万世之幸也。若周公则其身既不幸矣。而因事实之讹谬。遂为天下万世之大不幸。以复辟为践阼而王莽借之。几移汉鼎。以居东为东征而唐太宗假之。蹀血禁门。呜呼。使管蔡止于流言而已。则其心不过倾周公之位而夺周公之权而已。周公岂肯容心于其间哉。苟得毋毁王室则幸矣。苟得保全成王则幸矣。此鸱鸮诗之意也。假使成王终不悟。亦不过优游东郊。安得天分而已。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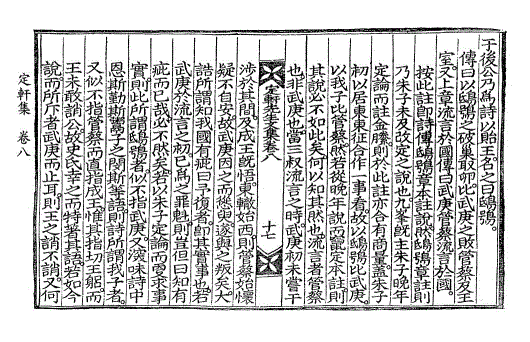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传曰以鸱鸮之破巢取卵。比武庚之败管蔡及王室。又上章流言于国传曰武庚管蔡流言于国。
按此注即诗传鸱鸮章本注说。然鸱鸮章注则乃朱子未及改定之说也。九峰既主朱子晚年定论而注金縢。则于此注亦合有商量。盖朱子初以居东东征合作一事看。故以鸱鸮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然若从晚年说而窜定本注。则其说必不如此矣。何以知其然也。流言者管蔡也。非武庚也。当三叔流言之时。武庚初未尝干涉于其间。及成王既悟。东辙始西。则管蔡始怀疑不自安。故武庚因之而怂臾。遂与之叛矣。大诰所谓知我国有疵曰予复者。即其实事也。若武庚于流言之初。已为之罪魁。则岂但曰知有疵而已哉。必不然矣。若以朱子定论而更求事实。则此所谓鸱鸮者。似不指武庚。又深味诗中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等语。则诗所谓我子者。又似不指管蔡而直指成王。惟其指切王躬。而王未敢诮公。故史氏幸之而特著其语。若如今说。而所斥者武庚而止耳。则王之诮不诮。又何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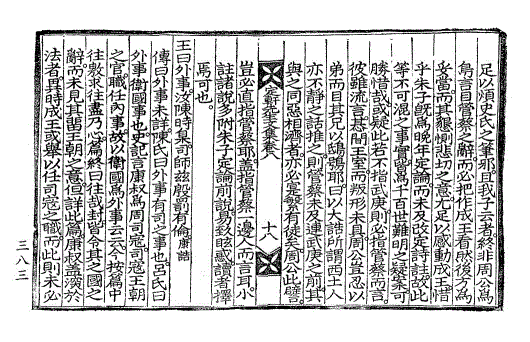 足以烦史氏之笔邪。且我子云者。终非周公为鸟言目管蔡之辞。而必把作成王看然后方为妥当。而其恳恻悲切之意。尤足以感动成王。惜乎朱子既为晚年定论。而未及改定诗注。故此等不可混之事实。皆为千百世难明之疑案。可胜惜哉。或疑此若不指武庚。则必指管蔡而言。彼虽流言。惎间王室。而叛形未具。周公岂忍以弟而目其兄以鸱鸮耶。曰以大诰所谓西土人亦不静之话推之。则管蔡未及连武庚之前。其与之同恶相济者。亦必寔繁有徒矣。周公此譬。岂必直指管蔡耶。盖指管蔡一边人而言耳。小注诸说多附朱子定论前说。易致眩惑。读者择焉可也。
足以烦史氏之笔邪。且我子云者。终非周公为鸟言目管蔡之辞。而必把作成王看然后方为妥当。而其恳恻悲切之意。尤足以感动成王。惜乎朱子既为晚年定论。而未及改定诗注。故此等不可混之事实。皆为千百世难明之疑案。可胜惜哉。或疑此若不指武庚。则必指管蔡而言。彼虽流言。惎间王室。而叛形未具。周公岂忍以弟而目其兄以鸱鸮耶。曰以大诰所谓西土人亦不静之话推之。则管蔡未及连武庚之前。其与之同恶相济者。亦必寔繁有徒矣。周公此譬。岂必直指管蔡耶。盖指管蔡一边人而言耳。小注诸说多附朱子定论前说。易致眩惑。读者择焉可也。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玆殷罚有伦。(康诰)
传曰外事未详。陈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吕氏曰外事卫国事也。史记言康叔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职任内事。故以卫国为外事云云。今按篇中往敷求往尽乃心。篇终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国之辞。而未见其留王朝之意。但详此篇。康叔盖深于法者。异时成王或举以任司寇之职。而此则未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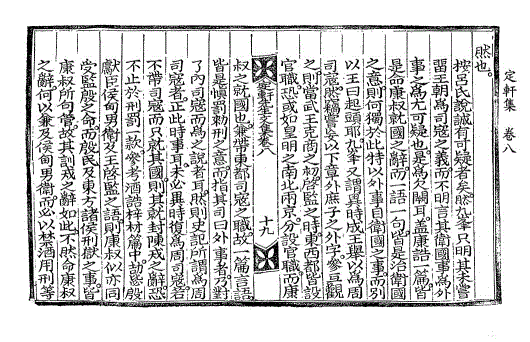 然也。
然也。按吕氏说诚有可疑者矣。然九峰只明其未尝留王朝为司寇之义。而不明言其卫国事为外事之为尤可疑也。是为欠阙耳。盖康诰一篇。皆是命康叔就国之辞。而一语一句。皆是治卫国之意。则何独于此特以外事目卫国之事。而别以王曰起头耶。九峰又谓异时成王举以为周司寇。然窃尝妄以下章外庶子之外字。参互观之。则当武王克商之初。启监之时。东西都皆设官职。恐或如皇明之南北两京。分设官职。而康叔之就国也。兼带东都司寇之职。故一篇言语。皆是慎罚敕刑之意。而指其司曰外事者。乃对了内司寇而为之说者耳。然则史记所谓为周司寇者。正此时事耳。未必异时复为周司寇。若不带司寇而只就其国。则其就封陈戒之辞。恐不止于刑罚一款。参考酒诰梓材篇中。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及王启监之语。则康叔似亦同受监殷之命。而殷民及东方诸侯刑狱之事。皆康叔所句管。故其训戒之辞如此。不然命康叔之辞。何以兼及侯甸男卫。而必以禁酒用刑等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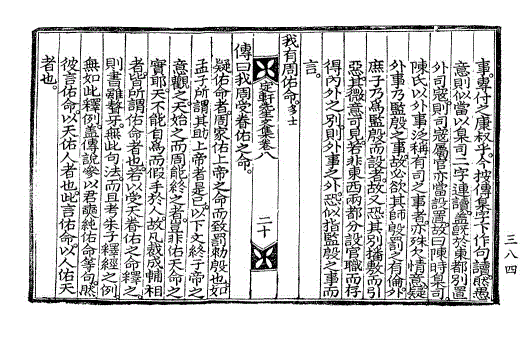 事。专付之康叔乎。今按传臬字下作句读。然愚意则似当以臬司二字连读。盖既于东都别置外司寇。则司寇属官亦当设置。故曰陈时臬司。陈氏以外事泛称有司之事者。亦殊欠情意。疑外事乃监殷之事。故必欲其师殷罚之有伦。外庶子乃为监殷而设者。故又恐其别播敷而引恶。其微意可见。若非东西两都分设官职而存得内外之别。则外事之外。恐似指监殷之事而言。
事。专付之康叔乎。今按传臬字下作句读。然愚意则似当以臬司二字连读。盖既于东都别置外司寇。则司寇属官亦当设置。故曰陈时臬司。陈氏以外事泛称有司之事者。亦殊欠情意。疑外事乃监殷之事。故必欲其师殷罚之有伦。外庶子乃为监殷而设者。故又恐其别播敷而引恶。其微意可见。若非东西两都分设官职而存得内外之别。则外事之外。恐似指监殷之事而言。我有周佑命。(多士)
传曰我周受眷佑之命。
疑佑命者。周家佑上帝之命而致罚敕殷也。如孟子所谓其助上帝者是已。以下文终于帝之意观之。天始之而周能终之者。岂非佑天命之实耶。天不能自为而假手于人。故凡裁成辅相者。皆所谓佑命者也。若以受天眷佑之命释之。则书虽聱牙。无此句法。而且考朱子释经之例。无如此释例。盖传说参以君奭纯佑命等句。然彼言佑命。以天佑人者也。此言佑命。以人佑天者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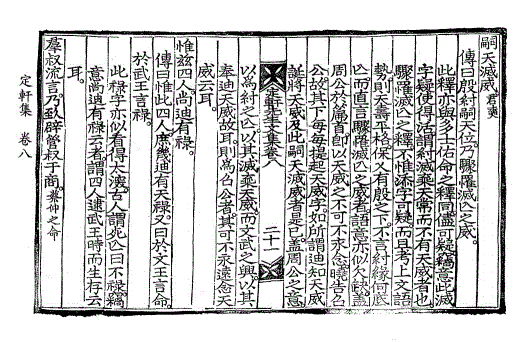 嗣天灭威。(君奭)
嗣天灭威。(君奭)传曰殷纣嗣天位。乃骤罹灭亡之威。
此释亦与多士佑命之释同。尽可疑。窃意此灭字疑使得活。谓纣灭弃天常而不有天威者也。骤罹灭亡之释。不惟添字可疑。而且考上文语势。则天寿平格。保乂有殷之下。不言纣缘何底亡。而直言骤罹灭亡之威者。语意亦似欠缺。盖周公于篇首。即以天威之不可不永念。晓告召公。故其下每每提起天威字。如所谓迪知天威诞将天威及此嗣天灭威者是已。盖周公之意。以为纣之亡。以其灭弃天威。而文武之兴。以其奉迪天威故耳。则为召公者。其可不永远念天威云耳。
惟玆四人。尚迪有禄。
传曰惟此四人。庶几迪有天禄。又曰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禄。
此禄字亦似看得太深。古人谓死亡曰不禄。窃意尚迪有禄云者。谓四人逮武王时而生存云耳。
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蔡仲之命)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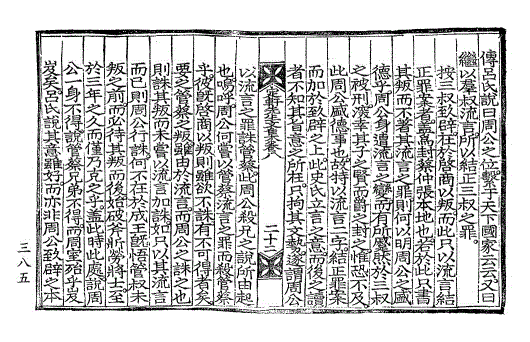 传吕氏说曰周公之位。系于天下国家云云。又曰继以群叔流言。所以结正三叔之罪。
传吕氏说曰周公之位。系于天下国家云云。又曰继以群叔流言。所以结正三叔之罪。按三叔致辟。在于启商以叛。而此只以流言结正罪案者。盖为封蔡仲张本地也。若于此只书其叛而不著其流言之罪。则何以明周公之盛德乎。周公身遭流言之变。而有所蹙然于三叔之被刑。深幸其子之贤而爵之封之。惟恐不及。此周公盛德事也。故特以流言二字。结正罪案而加于致辟之上。此史氏立言之意。而后之读者不知其旨意之所在。只拘其文势。遂谓周公以流言之罪诛管蔡。此周公杀兄之说所由起也。呜呼。周公何尝以管蔡流言之罪而杀管蔡乎。彼既启商以叛则虽欲不诛。有不可得者矣。要之管蔡之叛。虽由于流言。而周公之诛之也则诛其叛而未尝以流言加诛。如只以其流言而已则周公行诛。何不在于成王既悟管叔未叛之前。而必待其叛而后。始破斧斨劳将士。至于三年之久而仅乃克之乎。盖此时此处。说周公一身不得。说管蔡兄弟不得。而周室殆乎岌岌矣。吕氏说其意虽好。而亦非周公致辟之本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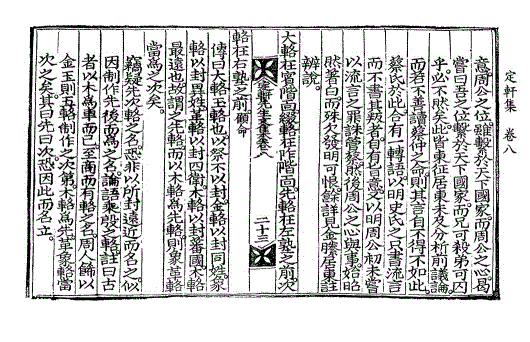 意。周公之位。虽系于天下国家。而周公之心。曷尝曰吾之位系于天下国家。而兄可杀弟可囚乎。必不然矣。此皆东征居东未及分析前议论。而若不善读蔡仲之命。则其言自不得不如此。蔡氏于此。合有一转语。以明史氏之只书流言而不书其叛者。自有旨意。又以明周公初未尝以流言之罪诛管蔡。然后周公之心与事。始昭然著白。而殊欠发明可恨。馀详见金縢居东注辨说。
意。周公之位。虽系于天下国家。而周公之心。曷尝曰吾之位系于天下国家。而兄可杀弟可囚乎。必不然矣。此皆东征居东未及分析前议论。而若不善读蔡仲之命。则其言自不得不如此。蔡氏于此。合有一转语。以明史氏之只书流言而不书其叛者。自有旨意。又以明周公初未尝以流言之罪诛管蔡。然后周公之心与事。始昭然著白。而殊欠发明可恨。馀详见金縢居东注辨说。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顾命)
传曰大辂玉辂也。以祭不以封。金辂以封同姓。象辂以封异姓。革辂以封四卫。木辂以封蕃国。木辂最远也。故谓之先辂。而以木辂为先辂。则象革辂当为之次矣。
窃疑先次辂之名。恐非以所封远近而名之。似因制作先后而为之名。论语乘殷之辂。注曰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周人饰以金玉则五辂制作之次第。木辂为先。革象辂当次之矣。其曰先曰次。恐因此而名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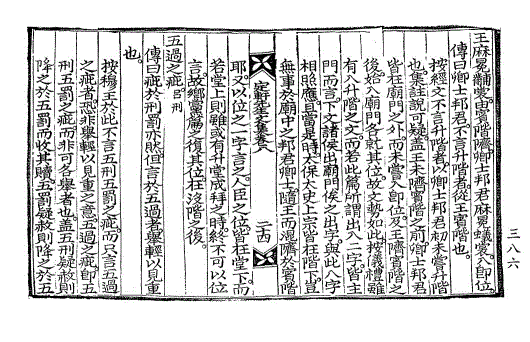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传曰卿士邦君。不言升阶者。从王宾阶也。
按经文不言升阶者。以卿士邦君初未尝升阶也。集注说可疑。盖王未隮宾阶之前。卿士邦君皆在庙门之外。而未尝入即位。及王隮宾阶之后。始入庙门各就其位。故文势如此。按仪礼虽有入升阶之文。而若此篇所谓出入二字。皆主门而言。下文诸侯出庙门俟之出字。与此入字相照应。且当是时。太保太史上宗皆在阶下。岂无事于庙中之邦君卿士。随王而混隮于宾阶耶。又以位之一字言之。人臣之位。皆在堂下。而若堂上则虽或有升堂成拜之时。终不可以位言。故乡党篇之复其位。在没阶之后。
五过之疵。(吕刑)
传曰疵于刑罚亦然。但言于五过者。举轻以见重也。
按穆王于此不言五刑五罚之疵。而只言五过之疵者。恐非举轻以见重之意。五过之疵。即五刑五罚之疵。而非可各举者也。盖五刑疑赦则降之于五罚而收其赎。五罚疑赦则降之于五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八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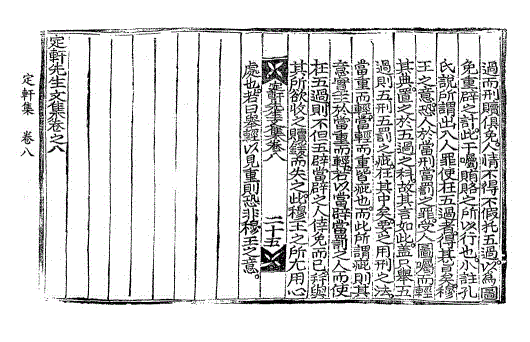 过而刑赎俱免。人情不得不假托五过。以为图免重辟之计。此干嘱贿赂之所以行也。小注孔氏说所谓出入人罪使在五过者。得其旨矣。穆王之意。恐人于当刑当罚之罪。受人图嘱而轻其典。置之于五过之科。故其言如此。盖只举五过则五刑五罚之疵。在其中矣。要之用刑之法。当重而轻。当轻而重皆疵也。而此所谓疵则其意实主于当重而轻。若以当辟当罚之人而使在五过。则不但五辟当辟之人倖免而已。并与其所欲收之赎锾而失之。此穆王之所尤用心处也。若曰举轻以见重则恐非穆王之意。
过而刑赎俱免。人情不得不假托五过。以为图免重辟之计。此干嘱贿赂之所以行也。小注孔氏说所谓出入人罪使在五过者。得其旨矣。穆王之意。恐人于当刑当罚之罪。受人图嘱而轻其典。置之于五过之科。故其言如此。盖只举五过则五刑五罚之疵。在其中矣。要之用刑之法。当重而轻。当轻而重皆疵也。而此所谓疵则其意实主于当重而轻。若以当辟当罚之人而使在五过。则不但五辟当辟之人倖免而已。并与其所欲收之赎锾而失之。此穆王之所尤用心处也。若曰举轻以见重则恐非穆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