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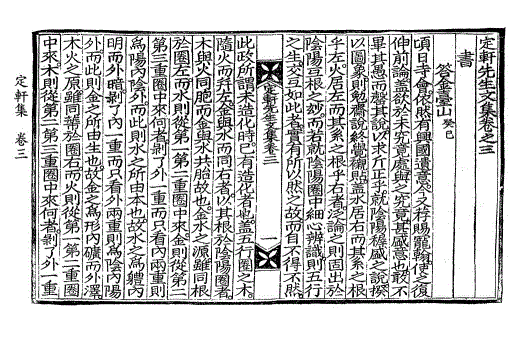 答金台山(癸巳)
答金台山(癸巳)顷日寺会。依然有兴国遗意。今又荐赐宠翰。使之复伸前论。盖欲于未究竟处。与之究竟。甚盛意也。敢不毕其愚而罄其说。以求斤正乎。就阴阳稚盛之说。揆以图象。则勉斋说终觉衬贴。盖水居右而其系之根乎左。火居左而其系之根乎右者。泛论之则固出于阴阳互根之妙。而若就阴阳圈中细心辨识。则五行之生。交互如此者。实有所以然之故。而自不得不然。此政所谓未造化时。已有造化者也。盖五行圈之木。随火而并左。金与水而同右者。以其根于阴阳圈者。木与火同胞而金与水共胎故也。金水之源。虽同根于圈左。而水则从第一第二重圈中来。金则从第二第三重圈中来何者。剥了外一重而只看内两重则为阳内阴外。而此则水之所由本也。故水之为体内明而外暗。剥了内一重而只看外两重则为阴内阳外。而此则金之所由生也。故金之为形内矿而外泽。木火之原。虽同蒂于圈右。而火则从第一第二重圈中来。木则从第二第三重圈中来何者。剥了外一重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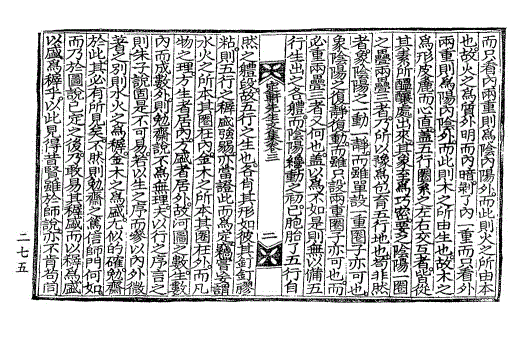 而只看内两重则为阴内阳外。而此则火之所由本也。故火之为质外明而内暗。剥了内一重而只看外两重则为阳内阴外。而此则木之所由生也。故木之为形皮粗而心直。盖五行圈系之左右交互者。皆从其素所酝酿处出来。其象至为巧密。要之阴阳一圈之叠两叠三者。乃所以豫为包育五行地也。苟非然者。象阴阳之一动一静。而虽单设一重圈子亦可也。象阴阳之复静复动。而虽只设两重圈子亦可也。而必重两叠三者又何也。盖以为不知是则无以备五行生出之各体。而阴阳才动之初。已胞胎了五行自然之体段。故五行之生也。各肖其形如彼其钉钉胶粘。则五行之稚盛强弱。亦当證此而为定。窃尝妄谓水火之所本其圈在内。金木之所本其圈在外。而凡物之理。方生者居内。方盛者居外。故河图之数。生数内而成数外。则勉斋说不为无理。夫以行之序言之则朱子说固是不可易。若以生之序而参以内外微著之别则水火之为稚。金木之为盛。尤似的确。勉斋于此。其必有所见矣。不然则勉斋之笃信师门何如。而乃于图说已定之后。乃敢易其稚盛而以稚为盛以盛为稚乎。以此见得昔贤虽于师说。亦不肯苟同
而只看内两重则为阴内阳外。而此则火之所由本也。故火之为质外明而内暗。剥了内一重而只看外两重则为阳内阴外。而此则木之所由生也。故木之为形皮粗而心直。盖五行圈系之左右交互者。皆从其素所酝酿处出来。其象至为巧密。要之阴阳一圈之叠两叠三者。乃所以豫为包育五行地也。苟非然者。象阴阳之一动一静。而虽单设一重圈子亦可也。象阴阳之复静复动。而虽只设两重圈子亦可也。而必重两叠三者又何也。盖以为不知是则无以备五行生出之各体。而阴阳才动之初。已胞胎了五行自然之体段。故五行之生也。各肖其形如彼其钉钉胶粘。则五行之稚盛强弱。亦当證此而为定。窃尝妄谓水火之所本其圈在内。金木之所本其圈在外。而凡物之理。方生者居内。方盛者居外。故河图之数。生数内而成数外。则勉斋说不为无理。夫以行之序言之则朱子说固是不可易。若以生之序而参以内外微著之别则水火之为稚。金木之为盛。尤似的确。勉斋于此。其必有所见矣。不然则勉斋之笃信师门何如。而乃于图说已定之后。乃敢易其稚盛而以稚为盛以盛为稚乎。以此见得昔贤虽于师说。亦不肯苟同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6H 页
 如此。然若学非勉斋。识非勉斋。则不若笃信师说之为寡过也。但勉斋说之附见于小注者。泛以生之序为言。而未尝解剥图体。指示其肯綮。故致论说之纷纭。年前偶读至此。得其说如此。而语涉创新。不敢自信矣。閤下一闻其说。遽赐颔可。或者其不甚谬戾矣乎。勉斋火生金之说。亦本于阴阳一圈而为之说者。而后来诸儒皆轻肆讥诋。然其特达之见则要不可少。并赐参订如何。昨呈拙韵飖飘二字。虽有珑玲之已例。而终觉未慊。故点改以呈。然其拙自如也。岂愈改愈好。非六一则不可也耶。昨论未及究竟者。更加别白。录在别纸。更赐订示如何。
如此。然若学非勉斋。识非勉斋。则不若笃信师说之为寡过也。但勉斋说之附见于小注者。泛以生之序为言。而未尝解剥图体。指示其肯綮。故致论说之纷纭。年前偶读至此。得其说如此。而语涉创新。不敢自信矣。閤下一闻其说。遽赐颔可。或者其不甚谬戾矣乎。勉斋火生金之说。亦本于阴阳一圈而为之说者。而后来诸儒皆轻肆讥诋。然其特达之见则要不可少。并赐参订如何。昨呈拙韵飖飘二字。虽有珑玲之已例。而终觉未慊。故点改以呈。然其拙自如也。岂愈改愈好。非六一则不可也耶。昨论未及究竟者。更加别白。录在别纸。更赐订示如何。别纸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刚义柔。仁阳义阴。则揆以上例。当曰义与仁。而此曰仁与义者。殊甚可疑。顷者妄以朱子说仰对。而谓恐当作义与仁矣。更思之。朱子说虽如此。而若本文果不差误。则圣人于此。别立义例者。当必有说。偶思得一说。似粗可通。盖兼三才而两之。则上与三为天。四与初为地。五与二为人。而天地则六与四皆阴。而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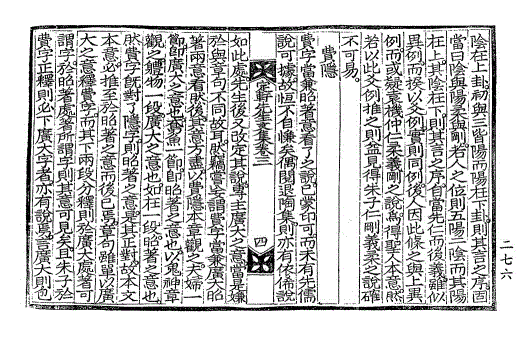 阴在上卦。初与三皆阳而阳在下卦。则其言之序。固当曰阴与阳柔与刚。若人之位则五阳二阴而其阳在上。其阴在下。则其言之序。自当先仁而后义。虽似异例。而揆以爻例。实则同例。后人因此条之与上异例。而或疑袁机仲仁柔义刚之说。为得圣人本意。然若以此爻例推之则益见得朱子仁刚义柔之说确不可易。
阴在上卦。初与三皆阳而阳在下卦。则其言之序。固当曰阴与阳柔与刚。若人之位则五阳二阴而其阳在上。其阴在下。则其言之序。自当先仁而后义。虽似异例。而揆以爻例。实则同例。后人因此条之与上异例。而或疑袁机仲仁柔义刚之说。为得圣人本意。然若以此爻例推之则益见得朱子仁刚义柔之说确不可易。费隐
费字当兼昭著意看了之说。已蒙印可。而未有先儒说可据。故恒不自慊矣。偶阅退陶集。则亦有依俙说如此处。先生后又改定其说。专主广大之意。当是嫌于与章句不同故耳。然窃尝妄谓费字当兼广大昭著两意看然后。其意方尽。以费隐本章观之。夫妇一节。即广大之意也。鸢鱼一节。即昭著之意也。以鬼神章观之。体物一段。广大之意也。如在一段。昭著之意也。然费字既对了隐字。则昭著之意。是其正对。故本文本意。必推至于昭著之意而后已焉。章句虽单以广大之意释费字。而其下两段分释则于广大处著可谓字。于昭著处著所谓字则其意可见矣。且朱子于费字正释则必下广大字者。亦有说焉。言广大则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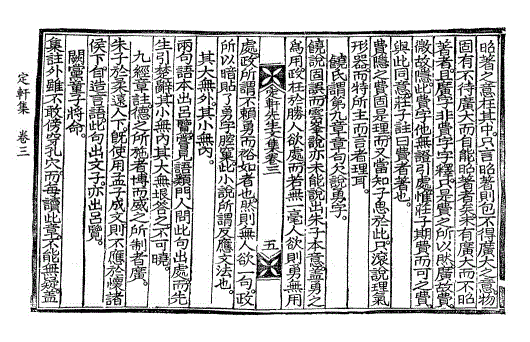 昭著之意在其中。只言昭著则包不得广大之意。物固有不待广大而自能昭著者矣。未有广大而不昭著者。且广字非费字字释。只是费之所以然。广故费。微哉隐。此费字他无證引处。惟庄子期费而可之费。与此同意。庄子注曰费者著也。
昭著之意在其中。只言昭著则包不得广大之意。物固有不待广大而自能昭著者矣。未有广大而不昭著者。且广字非费字字释。只是费之所以然。广故费。微哉隐。此费字他无證引处。惟庄子期费而可之费。与此同意。庄子注曰费者著也。费隐之费固是理。而又当知子思于此。只滚说理气形器。而特所主而言者理耳。
饶氏谓第九章章句欠说勇字。
饶说固误。而云峰说亦未能说出朱子本意。盖勇之为用。政在于胜人欲处。而若无一毫人欲则勇无用处。政所谓不赖勇而裕如者也。然则无人欲一句。政所以暗贴了勇字腔窠。此小说所谓反应文法也。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两句语本出吕览。尝见语类门人问此句出处。而先生引楚辞其小无内其大无垠答之。不可晓。
九经章注。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
朱子于柔远人下。既使用孟子成文。则不应于怀诸侯下。自造言语。此句出文子。亦出吕览。
阙党童子将命。
集注外虽不敢傍穿孔穴。而每读此章。不能无疑。盖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7L 页
 此将命。若果圣人欲其抑而教之而使之传命。则下文夫子所答。不合只陈其失而略不及此意。窃尝妄疑将命非夫子使之也。童子进见时。使人将命耳。按少仪有幼少者不将命之文。盖童幼者始见长者。只随人后入见。而不敢特使人将命。礼意然也。而此童子不循此礼。有此唐突之事。故或人适在门见其然。心怀怪讶矣。及童子退出后。入见夫子而问曰俄者进见之童子。果为请益而来乎。夫子遂即所见告之以此。盖其欲速之病。不但居位并行为然。而已先现于将命之初。
此将命。若果圣人欲其抑而教之而使之传命。则下文夫子所答。不合只陈其失而略不及此意。窃尝妄疑将命非夫子使之也。童子进见时。使人将命耳。按少仪有幼少者不将命之文。盖童幼者始见长者。只随人后入见。而不敢特使人将命。礼意然也。而此童子不循此礼。有此唐突之事。故或人适在门见其然。心怀怪讶矣。及童子退出后。入见夫子而问曰俄者进见之童子。果为请益而来乎。夫子遂即所见告之以此。盖其欲速之病。不但居位并行为然。而已先现于将命之初。答金台山别纸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集注云云。大抵名实二字正相反。而集注串合为说。故依而读之。终不能无疑。窃谓此二字当分开看。盖髡之为人。即尹士,彭更之类。见孟子历聘而无所施为。疑其有名而无实。故以名实拈起话头。先名实者。谓实先于名。有志于利人者也。后名实者。谓实后于名。有志于自利者也。在三卿之中名当句。言孟子在齐国诸卿中。最有声誉也。实未加于上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8H 页
 言事功不及于正君济民也。此或可备一说否。凡言先者对后之称。凡言后者对先之称。今合言名实则以名实为先者。所后何物。以名实为后者。所先何物。此是合思量处。
言事功不及于正君济民也。此或可备一说否。凡言先者对后之称。凡言后者对先之称。今合言名实则以名实为先者。所后何物。以名实为后者。所先何物。此是合思量处。以名与实相对则固不无所先所后何物之疑。而若如集注所释则自无此疑矣。且孟子之文。细腻恰似后世文章。无字数不足处。若名实两字。果如盛辨。则两字之间。当必有琐字助语。而决不但如是而已也。以声名事功谓之名实者。自是战国时言语如此。按庄子人间世篇。以䕺枝胥敖二国之用兵不止而谓是皆求名实之过云尔。则此名实字。政使得如此。取考如何。(名实字又见史记楚世家。)
大学顾諟注。或曰审也。諟之为审。见于何书。
白虎通曰审諟天地。疑本于此。
答郑参判(鸿庆)
客秋因递擎书。合即修覆。而穷里苦无京洛便。迄玆未果。负悚曷极。居然岁翻。春且向暮。伏未审台体动止万崇。而经衔尚带否。出入 迩英。沃赞 睿猷。平日所得。正惟此处用得。 圣学高明。问质出人意表云。固是天纵。而又安知非诸老成裨益弘多之力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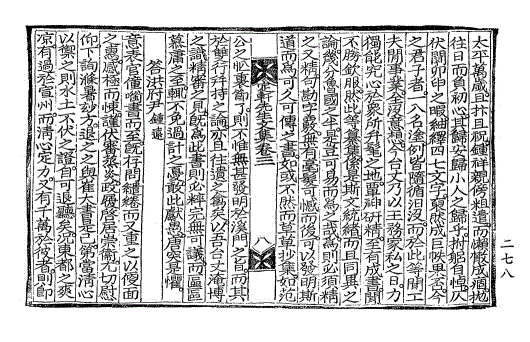 太平万岁。且抃且祝。钟祥亲傍粗遣。而懒散成痼。抛往日而负初心。其归安归小人之归乎。拊躬自悼。仄伏闻卯申之暇。䌷绎四七文字。裒然成巨帙果否。今之君子者。一入名涂。例皆随循汩没。而于此等閒工夫閒事业。全没意想。今台丈乃以王务家私之日。力独能究心于众所弁髦之地。覃神研精。至有成书。闻不胜钦服。然此等纂集。系是斯文统绪。而且同异之论。几分鲁国之半。是岂可易而为之哉。为则必须精之又精。句勘字覈。无有毫发可憾而后。可以发明斯道而为可久可传之书。如或不然而草草抄集。如范公之忙里节了。则不惟无甚发明于溪门之旨。而其于双行并持之论。亦且往遗之禽矣。以吾台丈淹博之识精审之见。既为此书则必粹完无可议。而区区慕庸之至。辄不免过计之忧。敢此献愚。唐突是惧。
太平万岁。且抃且祝。钟祥亲傍粗遣。而懒散成痼。抛往日而负初心。其归安归小人之归乎。拊躬自悼。仄伏闻卯申之暇。䌷绎四七文字。裒然成巨帙果否。今之君子者。一入名涂。例皆随循汩没。而于此等閒工夫閒事业。全没意想。今台丈乃以王务家私之日。力独能究心于众所弁髦之地。覃神研精。至有成书。闻不胜钦服。然此等纂集。系是斯文统绪。而且同异之论。几分鲁国之半。是岂可易而为之哉。为则必须精之又精。句勘字覈。无有毫发可憾而后。可以发明斯道而为可久可传之书。如或不然而草草抄集。如范公之忙里节了。则不惟无甚发明于溪门之旨。而其于双行并持之论。亦且往遗之禽矣。以吾台丈淹博之识精审之见。既为此书则必粹完无可议。而区区慕庸之至。辄不免过计之忧。敢此献愚。唐突是惧。答洪府尹(钟远)
意表官僮㘅书而至。既存问缱绻而又重之以便面之惠。感极而悚。谨伏审蒸炎。政履启居崇卫。尤切慰仰。下询涤暑妙方。退之之与崔大书是已。第当清心以御之则水土不伏之證。自可退听矣。况东都之爽凉。有过于宣州。而清心定力。又有千万于彼者。则即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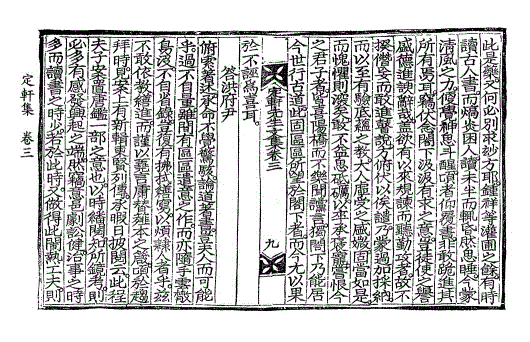 此是药。又何必别求妙方耶。钟祥等灌圃之馀。有时读古人书。而熇炎困人。读未半而辄昏然思睡。今蒙清风之力。便觉神思斗醒。顷者仰覆书。非敢跪进其所有焉耳。窃伏念閤下汲汲有求之意。岂徒使之誉盛德进谀辞哉。盖欲有以来规谏而听勤攻者。故不揆僭妄而敢进瞽说。方俯伏以俟谴。乃蒙过加采纳。而以至有验底蕴之教。大人虚受之盛美。固当如是。而愧惧则深矣。敢不益思砥砺。以卒承褒宠。尝恨今之君子者。皆喜阳桥而不乐闻谠言。独閤下乃能居今世行古道。此固区区所望于閤下者。而今尤以果于不诬为喜耳。
此是药。又何必别求妙方耶。钟祥等灌圃之馀。有时读古人书。而熇炎困人。读未半而辄昏然思睡。今蒙清风之力。便觉神思斗醒。顷者仰覆书。非敢跪进其所有焉耳。窃伏念閤下汲汲有求之意。岂徒使之誉盛德进谀辞哉。盖欲有以来规谏而听勤攻者。故不揆僭妄而敢进瞽说。方俯伏以俟谴。乃蒙过加采纳。而以至有验底蕴之教。大人虚受之盛美。固当如是。而愧惧则深矣。敢不益思砥砺。以卒承褒宠。尝恨今之君子者。皆喜阳桥而不乐闻谠言。独閤下乃能居今世行古道。此固区区所望于閤下者。而今尤以果于不诬为喜耳。答洪府尹
俯索著述。承命不觉惊骇。论道著书。岂夫人而可能乎。过不自量。虽间有区区遣意之作。而亦随手云散鸟没。不自省录。岂复有拂拭缮写。以烦隶人者乎。玆不敢依教缮进。而谨以荛言庸替薤本之箴。顷于趋拜时。见案上有新辑东贤列传。承暇日披阅云。此程夫子案置唐鉴一部之意也。以时翻阅。知所镜考。则必多有感发兴起之端。然窃意邑剧讼健。治事之时多而读书之时少。若于此时。又做得此闹热工夫。则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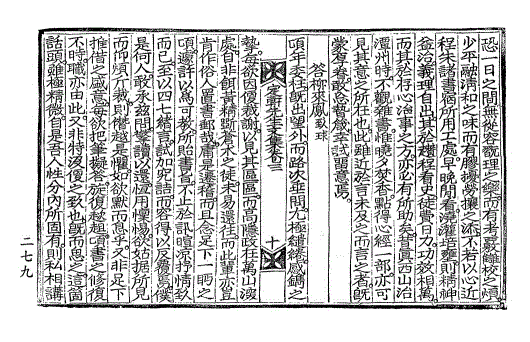 恐一日之间。无从容玩理之乐。而有考覈雠校之烦。少平融清和之味而有胶扰劳攘之添。不若以心近程朱诸书宿所用工处。早晚閒看。浇灌培壅。则精神益治。义理自出。其于趱程看史。徒费日力。功效相万。而其于存心治事之方。亦必有所助矣。昔真西山治潭州时。不观杂书。惟晓夕焚香。点得心经一部。亦可见其意之所在也。此虽近于言未及之而言之者。既蒙厚眷。敢忘亵箴。幸试留意焉。
恐一日之间。无从容玩理之乐。而有考覈雠校之烦。少平融清和之味而有胶扰劳攘之添。不若以心近程朱诸书宿所用工处。早晚閒看。浇灌培壅。则精神益治。义理自出。其于趱程看史。徒费日力。功效相万。而其于存心治事之方。亦必有所助矣。昔真西山治潭州时。不观杂书。惟晓夕焚香。点得心经一部。亦可见其意之所在也。此虽近于言未及之而言之者。既蒙厚眷。敢忘亵箴。幸试留意焉。答柳来凤(致球)
顷年委枉。既出望外。而路次垂问。尤极缱绻。感镌之挚。每欲因便裁谢。以见其区区。而高隐政在万山深处。自非饵黄精斲苍朮之徒。未易还往。而此辈亦岂肯作俗人置书邮哉。庸是迁稽。而且念足下一眄之顷。遽许以为可教。所贻书旨。不止于讯暄凉抒情致而已。至以四七绪言。试加究诘。而容得以反覆焉。仆是何人。敢承玆问。擎读以还。恒用懔惕。欲姑据所见而仰烦斤裁。则僭越是惧。如欲默而息乎。又非足下推借之盛意。每欲把笔拟答。旋复趑趄。顷书之修复不时。职亦由此。又非特没便之致也。既而思之。这个话头。虽极精微。自是吾人性分内所固有。则私相讲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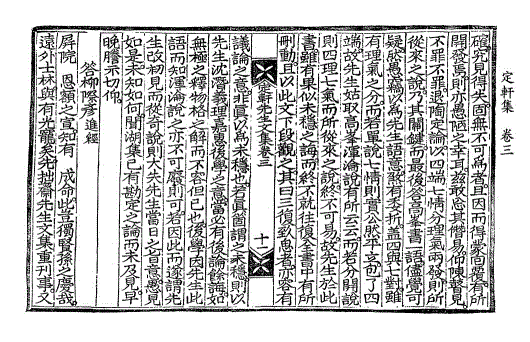 确。究见得失。固无不可为者。且因而得蒙回覆。有所开发焉。则亦愚陋之幸耳。玆敢忘其僭易。仰陈瞽见。不罪不罪。退陶定论。以四端七情分理气两发。则所从来之说。乃其关键。而最后答高峰书一语。尽觉可疑。然愚窃以为先生语意。煞有委折。盖四与七对。虽有理气之分。而若单说七情则实公然平立。包了四端。故先生姑取高峰浑沦说有所云云。而若分开说则四理七气而所从来之说。终不可易。故先生于此书。虽有果似未稳之诲。而终不就往复全书中有所删动。且以此文下段观之。其曰三复致思者。亦容有议论之意。非真以为未稳也。若真个谓之未稳。则以先生沈潜义理嘉惠后学之意。当必有后论馀诲。如无极之释物格之解而不容但已也。后学因先生此语而知浑沦说之亦不可废则可。若因此而遂谓先生改初见而从奇说则大失先生当日之旨意。愚见如是。未知如何。闻湖集已有勘定之论而未及见。早晚誊示切仰。
确。究见得失。固无不可为者。且因而得蒙回覆。有所开发焉。则亦愚陋之幸耳。玆敢忘其僭易。仰陈瞽见。不罪不罪。退陶定论。以四端七情分理气两发。则所从来之说。乃其关键。而最后答高峰书一语。尽觉可疑。然愚窃以为先生语意。煞有委折。盖四与七对。虽有理气之分。而若单说七情则实公然平立。包了四端。故先生姑取高峰浑沦说有所云云。而若分开说则四理七气而所从来之说。终不可易。故先生于此书。虽有果似未稳之诲。而终不就往复全书中有所删动。且以此文下段观之。其曰三复致思者。亦容有议论之意。非真以为未稳也。若真个谓之未稳。则以先生沈潜义理嘉惠后学之意。当必有后论馀诲。如无极之释物格之解而不容但已也。后学因先生此语而知浑沦说之亦不可废则可。若因此而遂谓先生改初见而从奇说则大失先生当日之旨意。愚见如是。未知如何。闻湖集已有勘定之论而未及见。早晚誊示切仰。答柳际彦(进经)
屏院 恩额之宣。知有 成命。此岂独贤孙之庆哉。远外士林。与有光宠矣。先拙斋先生文集重刊事。又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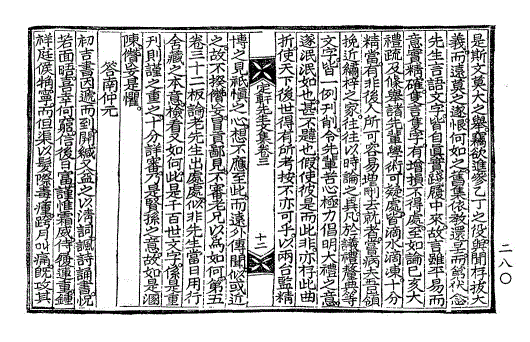 是斯文莫大之举。窃欲进参乙丁之役。与闻存拔大义。而远莫之遂。恨何如之。旧集依教还呈。而第伏念先生言语文字。皆自真实践履中来。故言虽平易而意实精确。只言只字。有增损不得处。至如论己亥大礼疏及条举诸先辈学术可疑处。皆滴水滴冻。十分精当。有非后人所可容易增删去就者。尝病夫吾岭挽近绣梓之家。往往以时论之异。凡于议礼釐典等文字。皆一例刊削。令先辈苦心极力倡明大礼之意。遂泯泯如也。甚不韪也。假使彼是而此非。亦存此曲折。使天下后世得有所考按不亦可乎。以两台监精博之见祇慎之心。想不应至此。而远外传闻。似或近之。故不揆僭妄。冒贡鄙见。不审老兄以为如何。第五卷三十二板论老先生出处处。似非先生当日用行舍藏之本意。检看又如何。此是千百世文字。系是重刊则谨之重之。十分详审。乃是贤孙之意。故如是溷陈。僭妄是惧。
是斯文莫大之举。窃欲进参乙丁之役。与闻存拔大义。而远莫之遂。恨何如之。旧集依教还呈。而第伏念先生言语文字。皆自真实践履中来。故言虽平易而意实精确。只言只字。有增损不得处。至如论己亥大礼疏及条举诸先辈学术可疑处。皆滴水滴冻。十分精当。有非后人所可容易增删去就者。尝病夫吾岭挽近绣梓之家。往往以时论之异。凡于议礼釐典等文字。皆一例刊削。令先辈苦心极力倡明大礼之意。遂泯泯如也。甚不韪也。假使彼是而此非。亦存此曲折。使天下后世得有所考按不亦可乎。以两台监精博之见祇慎之心。想不应至此。而远外传闻。似或近之。故不揆僭妄。冒贡鄙见。不审老兄以为如何。第五卷三十二板论老先生出处处。似非先生当日用行舍藏之本意。检看又如何。此是千百世文字。系是重刊则谨之重之。十分详审。乃是贤孙之意。故如是溷陈。僭妄是惧。答南仲元
初吉书因递而到。开缄又益之以清词。讽诗诵书。恍若面晤。喜幸何穷。信后日富。谨惟霜威。侍履连重。钟祥庭候觕宁。而但渠以发际毒尰。跨月叫痛。既攻其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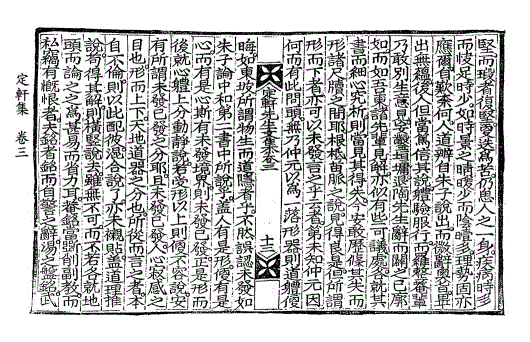 坚。而瑕者复坚。更迭为苦。仍思人之一身。疾病时多而快足时少。如时景之晴暖少而阴曀多。理势固亦应尔。自叹柰何。人道辨自朱子说出。而微辞奥旨。毕出无蕴。后人但当笃信其说。体验服行。而罗整庵辈乃敢别生意见。妄凿垣墉。退陶先生辞而辟之已廓如。而如吾东诸先辈见解。亦似有些可议处。各就其书而细心究析。则当见其得失。今安敢历条其失而形诸尺牍之间耶。根柢苗脉之说。见得良是。但所谓形而下者亦可以未发言之乎云者。第未知仲元因何而有此问头。无乃仲元以为一落形器则道体便晦。如东坡所谓物生而道隐者乎。不然误认未发如朱子论中和第二书中所说乎。盖人有是形。便有是心。而有是心斯有未发境界。则未发已发。正是形而后就心体上分动静说。若受形以上则便不容说。安有所谓未发已发之分耶。且未发已发。人心寂感之目也。形而上下。天地道器之分也。所从而言之者。本自不伦。则以此配彼。混合说了。亦未衬贴。盖道理推说。苟得其解。则横竖说去。虽无不可。而不若各就地头而论之之为甚易而省力耳。庵铭当斲削副教。而私窃有慨恨者。夫铭者铭而自警之辞。汤之盘铭。武
坚。而瑕者复坚。更迭为苦。仍思人之一身。疾病时多而快足时少。如时景之晴暖少而阴曀多。理势固亦应尔。自叹柰何。人道辨自朱子说出。而微辞奥旨。毕出无蕴。后人但当笃信其说。体验服行。而罗整庵辈乃敢别生意见。妄凿垣墉。退陶先生辞而辟之已廓如。而如吾东诸先辈见解。亦似有些可议处。各就其书而细心究析。则当见其得失。今安敢历条其失而形诸尺牍之间耶。根柢苗脉之说。见得良是。但所谓形而下者亦可以未发言之乎云者。第未知仲元因何而有此问头。无乃仲元以为一落形器则道体便晦。如东坡所谓物生而道隐者乎。不然误认未发如朱子论中和第二书中所说乎。盖人有是形。便有是心。而有是心斯有未发境界。则未发已发。正是形而后就心体上分动静说。若受形以上则便不容说。安有所谓未发已发之分耶。且未发已发。人心寂感之目也。形而上下。天地道器之分也。所从而言之者。本自不伦。则以此配彼。混合说了。亦未衬贴。盖道理推说。苟得其解。则横竖说去。虽无不可。而不若各就地头而论之之为甚易而省力耳。庵铭当斲削副教。而私窃有慨恨者。夫铭者铭而自警之辞。汤之盘铭。武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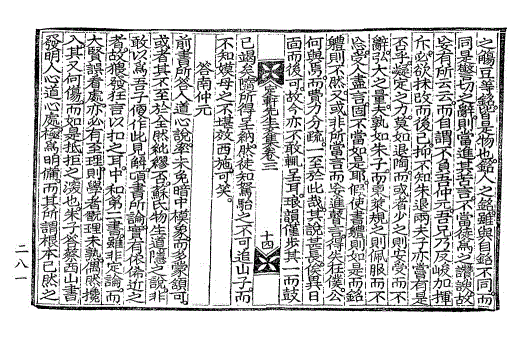 之觞豆等铭。皆是物也。铭人之铭。虽与自铭不同。而同是警切之辞。则当进其苦言。不当徒为之赞谀。故妄有所云云。而自谓不负吾仲元。吾兄乃反峻加挥斥。必欲抹改而后已。抑不知朱退两失子亦尝有是否乎。凝定之力。莫如退陶。而或者少之则安受而不辞。弘大之量。夫孰如朱子。而东莱规之则佩服而不忘。受人尽言。固不当如是耶。假使书体则如是而铭体则不然。又或非所当言而妄进瞽言。得失在仆。公何与焉。而费力分疏。一至于此哉。其说甚长。俟异日面而后可。故今亦不敢辄呈耳。琅韵仅步其一而鼓已竭矣。随所得呈纳。然徒知驽骀之不可追山子。而不知嫫母之不堪效西施。可笑。
之觞豆等铭。皆是物也。铭人之铭。虽与自铭不同。而同是警切之辞。则当进其苦言。不当徒为之赞谀。故妄有所云云。而自谓不负吾仲元。吾兄乃反峻加挥斥。必欲抹改而后已。抑不知朱退两失子亦尝有是否乎。凝定之力。莫如退陶。而或者少之则安受而不辞。弘大之量。夫孰如朱子。而东莱规之则佩服而不忘。受人尽言。固不当如是耶。假使书体则如是而铭体则不然。又或非所当言而妄进瞽言。得失在仆。公何与焉。而费力分疏。一至于此哉。其说甚长。俟异日面而后可。故今亦不敢辄呈耳。琅韵仅步其一而鼓已竭矣。随所得呈纳。然徒知驽骀之不可追山子。而不知嫫母之不堪效西施。可笑。答南仲元
前书所答人道心说。率未免暗中模象。而多蒙颔可。或者其不至于全然纰缪否。苏氏物生道隐之说。非敢以为吾子便作此见解。顷书所论。实有依俙近之者。故猥发狂言以扣之耳。中和第二书。虽非定论。而大贤误看处。亦必有至理。则学者玩理未熟。偶然搀入。其又何伤。而如是抵拒之深也。朱子答蔡西山书发明人心道心处。极为明备。而其所谓根本已然之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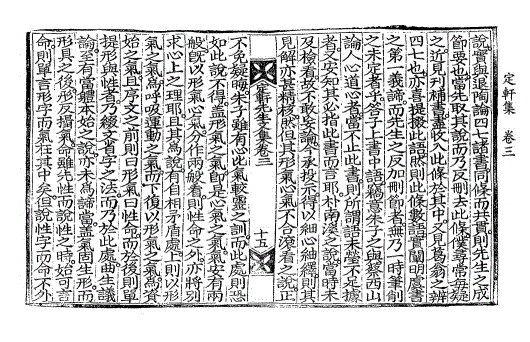 说。实与退陶论四七诸书。同条而共贯。则先生之成节要也。当先取其说而乃反删去此条。仆寻常每疑之。近见刊补书。尽收入此条于其中。又见葛翁之辨四七也。亦喜提掇此语。然则此条数语。实阐明虞书之第一义谛。而先生之反加删节者。无乃一时笔削之未定者乎。答子上书中语。窃意朱子之与蔡西山论人心道心者。当不止此书。则所谓语未莹不足据者。又安知其必指此书而言耶。朴南溪之说。当时未及检看。故不敢妄论。今承投示。得以细心䌷绎。则其见解亦甚精核。然但其形气心气不合滚看之说。正不免疑晦。朱子虽有心比气较灵之训。而此处则恐如此说不得。盖形气之气。即是心气之气。气安有两般。既以形气心气。分作两般看。则性命之外。亦将别求心上之理耶。且其为说。有自相矛盾处。上则以形气之气。为呼吸运动之气。而下复以形气之气。为资始之气。且序文之前则曰形气曰性命。而于后则单提形与性者。乃缀文省字之法。而乃于此处。曲生议论。至有当体本始之说。亦未为谛当。盖气固生形。而形具之后。形反摄气。命虽先性而说性之时。始可言命。则单言形字而气在其中矣。但说性字而命不外
说。实与退陶论四七诸书。同条而共贯。则先生之成节要也。当先取其说而乃反删去此条。仆寻常每疑之。近见刊补书。尽收入此条于其中。又见葛翁之辨四七也。亦喜提掇此语。然则此条数语。实阐明虞书之第一义谛。而先生之反加删节者。无乃一时笔削之未定者乎。答子上书中语。窃意朱子之与蔡西山论人心道心者。当不止此书。则所谓语未莹不足据者。又安知其必指此书而言耶。朴南溪之说。当时未及检看。故不敢妄论。今承投示。得以细心䌷绎。则其见解亦甚精核。然但其形气心气不合滚看之说。正不免疑晦。朱子虽有心比气较灵之训。而此处则恐如此说不得。盖形气之气。即是心气之气。气安有两般。既以形气心气。分作两般看。则性命之外。亦将别求心上之理耶。且其为说。有自相矛盾处。上则以形气之气。为呼吸运动之气。而下复以形气之气。为资始之气。且序文之前则曰形气曰性命。而于后则单提形与性者。乃缀文省字之法。而乃于此处。曲生议论。至有当体本始之说。亦未为谛当。盖气固生形。而形具之后。形反摄气。命虽先性而说性之时。始可言命。则单言形字而气在其中矣。但说性字而命不外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2L 页
 是。今乃以此分当体本始者说非不行。而既于序文少无发挥之益。徒有分析之劳。则何苦而添枝添叶。枉费辞说乎。且性命之命字。或可如此说。而以形气之气。为推原其本者。微觉牵强。盖但有口之形而无口之气。则必无朵食之念。只有鼻之形而无鼻之气则必无嗅香之性。此处又岂可离气与形。而以气为本始。以形为当体乎。又曰有此形气。故人心因之而生。有此性命。故道心因之而发。非理气互发之谓者亦几矣。而犹未免偏主之弊。盖理气互发之说。自本达支之论也。因而生发之说。从流溯源之论也。譬之于水。其流有清浊之别。而其清其浊。未有无其故而然者。故从流溯源者。既可曰浊生于彼。清原于此。则寻源沿流者。又岂不可曰此发而为清。彼发而为浊哉。同一话头而自末探本则以为可如此说。自本达支则以为不可如此说。此正言十不言二五之病。又不通之论也。但人心道心。微与四七面貌不同。故退陶夫子不于人心道心上。立互发之论。而但主四七说。彼为一边褊袒者。乃反舍却本来面目。而拖转人道上说。使骤而观之者。不无荧惑于其间。今不必杂采诸家说。但就先生本集。熟复而详玩。则先生所谓
是。今乃以此分当体本始者说非不行。而既于序文少无发挥之益。徒有分析之劳。则何苦而添枝添叶。枉费辞说乎。且性命之命字。或可如此说。而以形气之气。为推原其本者。微觉牵强。盖但有口之形而无口之气。则必无朵食之念。只有鼻之形而无鼻之气则必无嗅香之性。此处又岂可离气与形。而以气为本始。以形为当体乎。又曰有此形气。故人心因之而生。有此性命。故道心因之而发。非理气互发之谓者亦几矣。而犹未免偏主之弊。盖理气互发之说。自本达支之论也。因而生发之说。从流溯源之论也。譬之于水。其流有清浊之别。而其清其浊。未有无其故而然者。故从流溯源者。既可曰浊生于彼。清原于此。则寻源沿流者。又岂不可曰此发而为清。彼发而为浊哉。同一话头而自末探本则以为可如此说。自本达支则以为不可如此说。此正言十不言二五之病。又不通之论也。但人心道心。微与四七面貌不同。故退陶夫子不于人心道心上。立互发之论。而但主四七说。彼为一边褊袒者。乃反舍却本来面目。而拖转人道上说。使骤而观之者。不无荧惑于其间。今不必杂采诸家说。但就先生本集。熟复而详玩。则先生所谓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3H 页
 八窗玲珑者。尽不我欺矣。彼一种论说。但执理无情意之说。做出许多葛藤。论说纷然。然理无情意。气有作用。夫人而皆知之。众人所知。良遂庸讵有不知而必为此互发之说哉。其所以必立此说者。盖理虽无情意。而洁净之地。自有融泄底意。理虽无作用而冲漠之中。自有森然之象。故深见理气合一。相须互用之妙而立此说焉耳。苟非然者。朱子何以有理自有用之训。而又何以有四理七气两下说破之论哉。此其为说。十分精当。建质无悖。而祇缘栗谷拾高峰已弃之说。别立赤帜。后之和应者。至将已勘之讼。翻作未决之案。至若南溪之学。非不精且洽矣。而只是一个胡文定横在肚里。故凡所以疏释序文。出入理气者。似未免堕于一偏。深觉慨然。所示寂感道器混合为说。未见其不可者。终觉未稳。盖寂感则有分段有时节。道器则无分段无时节。道即是器。器即是道。而道与器只著如此说。更不可分段说。则岂可与寂感之有时节。有分段者。混合而为说也。太极稚盛之说。无人缮写。容俟后便。而庵铭非敢靳改。窃疑吾兄有周遮之病而无虚受之量。故自绌其书而不欲出。今见来示。吾兄实无他肠。又安敢胶守其初。谨当唯命。
八窗玲珑者。尽不我欺矣。彼一种论说。但执理无情意之说。做出许多葛藤。论说纷然。然理无情意。气有作用。夫人而皆知之。众人所知。良遂庸讵有不知而必为此互发之说哉。其所以必立此说者。盖理虽无情意。而洁净之地。自有融泄底意。理虽无作用而冲漠之中。自有森然之象。故深见理气合一。相须互用之妙而立此说焉耳。苟非然者。朱子何以有理自有用之训。而又何以有四理七气两下说破之论哉。此其为说。十分精当。建质无悖。而祇缘栗谷拾高峰已弃之说。别立赤帜。后之和应者。至将已勘之讼。翻作未决之案。至若南溪之学。非不精且洽矣。而只是一个胡文定横在肚里。故凡所以疏释序文。出入理气者。似未免堕于一偏。深觉慨然。所示寂感道器混合为说。未见其不可者。终觉未稳。盖寂感则有分段有时节。道器则无分段无时节。道即是器。器即是道。而道与器只著如此说。更不可分段说。则岂可与寂感之有时节。有分段者。混合而为说也。太极稚盛之说。无人缮写。容俟后便。而庵铭非敢靳改。窃疑吾兄有周遮之病而无虚受之量。故自绌其书而不欲出。今见来示。吾兄实无他肠。又安敢胶守其初。谨当唯命。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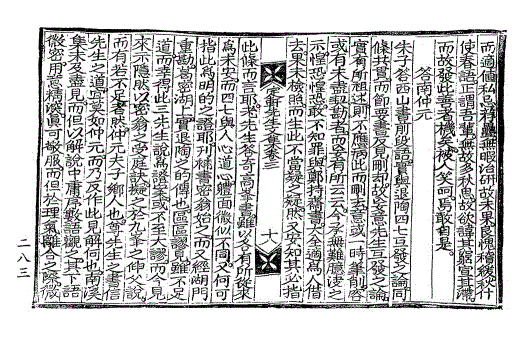 而适值私忌荐叠。无暇治研故未果。良愧稽缓。秋什使春语。正谓吾辈。无故多秋思。故欲讳其穷宣其滞。而故发此善者机矣。被人笑呵。焉敢自是。
而适值私忌荐叠。无暇治研故未果。良愧稽缓。秋什使春语。正谓吾辈。无故多秋思。故欲讳其穷宣其滞。而故发此善者机矣。被人笑呵。焉敢自是。答南仲元
朱子答西山书前段语。实与退陶四七互发之论。同条共贯。而节要书反见删却。故妄意先生互发之论。实有所祖述。则不应病此而删去。意或一时笔削。容或有未尽契勘者。而妄有所云云。今承无难臆决之示。惶恐惶恐。敢不知罪。与郑持斋书。大全适为人借去。果未检照。而生此不当疑之疑。然又安知其必指此条而言耶。老先生答奇高峰书。虽以各有所从来为未安。而四七与人心道心。体面微似不同。又何可指此为明的之證耶。刊补书密翁始之。而又经湖门重勘。葛密湖上。实退陶之的传也。区区谬见。虽不足道。而幸得此三先生说为證案。或不至大谬。而今见来示隐然以密翁之受庭诀。拟之于九峰之伸父说。而有若不足者然。仲元夫子乡人也。尊先生之书信先生之道。宜莫如仲元。而乃反作此见解何也。南溪集未及尽见。而但以解说中庸序数语观之。其下语微密。用意精深。真可敬服。而但于理气离合之际。微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4H 页
 有少出入处。而其要归指趣则似与溪门旨诀相倍。故不揆僭妄。索性缴破。而其语不觉其流入于悖耳。仲元规之是也。然朱子之尊信上蔡龟山不为不至。而于剖判义理处。则未尝少饶。而往往有辞意直截处。此又何也。自处过重之示。又似不相悉。仆于仲元信其不相外。故辄罄其狂劳花相。而于他人未尝敢出一口气。则仆何尝乃尔耶。且敖虽凶德。而犹有所挟故也。仆直一悾悾耳。敖他人犹不敢。况吾仲元乎。然朋友相规之言。如受人馈药。今虽未达而不即尝。然而他日病与药相对。则正好服食。岂可以见今病證之相左。而拜却万金之良药也耶。人道辨改本。于鄙意多有未契处。故逐条贡疑。更愿勿以前见为主而重加反覆也。看义理如啖荔支。剥了皮。又有肉。去了肉。又有浆。若才剥一重而遽然自足。则终无长进之时。仲元既不安于故而有此改本矣。则何独于此而靳改耶。切乞留意。
有少出入处。而其要归指趣则似与溪门旨诀相倍。故不揆僭妄。索性缴破。而其语不觉其流入于悖耳。仲元规之是也。然朱子之尊信上蔡龟山不为不至。而于剖判义理处。则未尝少饶。而往往有辞意直截处。此又何也。自处过重之示。又似不相悉。仆于仲元信其不相外。故辄罄其狂劳花相。而于他人未尝敢出一口气。则仆何尝乃尔耶。且敖虽凶德。而犹有所挟故也。仆直一悾悾耳。敖他人犹不敢。况吾仲元乎。然朋友相规之言。如受人馈药。今虽未达而不即尝。然而他日病与药相对。则正好服食。岂可以见今病證之相左。而拜却万金之良药也耶。人道辨改本。于鄙意多有未契处。故逐条贡疑。更愿勿以前见为主而重加反覆也。看义理如啖荔支。剥了皮。又有肉。去了肉。又有浆。若才剥一重而遽然自足。则终无长进之时。仲元既不安于故而有此改本矣。则何独于此而靳改耶。切乞留意。别纸
试以太极一图观之。太极生阴阳则太极即理也。阴阳即气也。太极未动之前。只是浑然一理而已。及其既动而阴阳始分。则岂可谓太极未动之前。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4L 页
 已有阴阳之气。与太极而并体乎。由是观之。人心之既发而善恶始分。从可见矣。
已有阴阳之气。与太极而并体乎。由是观之。人心之既发而善恶始分。从可见矣。太极图从有理而后有气处说下来。故大极未动之前。固不可辊说阴阳。而人心道心则乃从心体上分理气说了。则心者又岂但理无气底物事耶。此心未发之前。理虽占得境界。而气亦未尝不在。比之四时则冬至一阳未动之前。即人心未发境界也。于斯时也。虽万动俱息。归根复命。而谓之无气可乎。心虽未发。而其已局之形。已禀之气。则依然自在。未发之前。固无善恶之相对。而其为人道心之根柢苗脉。则固自有在矣。
人心未发之前。谓有天理之根柢则可。谓有人欲之根柢则不可。
人欲乃人心之流而失者也。朱子谓人心有根柢。未尝谓人欲有根柢。而此乃一之。恐考之未审。
程子曰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又曰谓之恶者本非恶。但过与不及便如此。朱子亦曰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来人欲。此极至之论也。
程朱此说。主性本善而言。非向人心道心上立说者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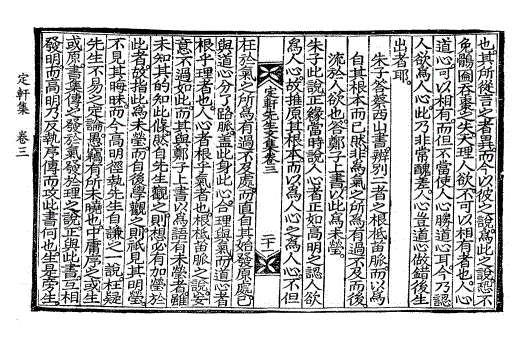 也。其所从言之者异。而今以彼之说。为此之说。恐不免鹘囵吞枣之失。天理人欲。不可以相有者也。人心道心。可以相有。而但不当使人心胜道心耳。今乃认人欲为人心。此乃非常丑差。人心岂道心做错后生出者耶。
也。其所从言之者异。而今以彼之说。为此之说。恐不免鹘囵吞枣之失。天理人欲。不可以相有者也。人心道心。可以相有。而但不当使人心胜道心耳。今乃认人欲为人心。此乃非常丑差。人心岂道心做错后生出者耶。朱子答蔡西山书。辨别二者之根柢苗脉。而以为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答郑子上书。以此为未莹。
朱子此说。正缘当时说人心者正如高明之认人欲为人心。故推原其根本。而以为人心之为人心。不但在于气之所为有过不及处。而直自其始发原处。已与道心分了路脉。盖此身此心。合理与气。而道心者根乎理者也。人心者根乎气者地。根柢苗脉之说。妄意不过如此。而其与郑子上书以为语有未莹者。虽未知其的知此条。然自先生观之。则想必有加莹于此者。故指此为未莹。而自后学观之。则祇见其明莹。不见其晦昧。而今高明径执先生自谦之一说。枉疑先生不易之定论。愚窃有所未晓也。中庸序之或生或原。书集传之发于气发于理之说。正与此书。互相发明。而高明乃反执序传而攻此书何也。生是旁生。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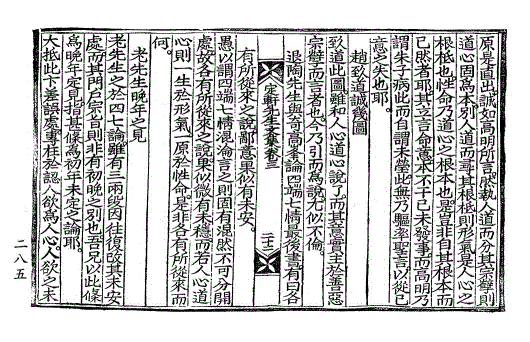 原是直出。诚如高明所言。然执人道而分其宗孽则道心固为本。别人道而寻其根柢则形气是人心之根柢也。性命乃道心之根本也。是岂非自其根本而已然者耶。其立言命意。本不干已未发事。而高明乃谓朱子病此而自谓未莹。此无乃驱率圣言。以从己意之失也耶。
原是直出。诚如高明所言。然执人道而分其宗孽则道心固为本。别人道而寻其根柢则形气是人心之根柢也。性命乃道心之根本也。是岂非自其根本而已然者耶。其立言命意。本不干已未发事。而高明乃谓朱子病此而自谓未莹。此无乃驱率圣言。以从己意之失也耶。赵致道诚几图
致道此图。虽和人心道心说了。而其意实主于善恶宗孽而言者也。今乃引而为说。尤似不伦。
退陶先生与奇高峰论四端七情最后书。有曰各有所从来之说。鄙意果似有未安。
愚以谓四端七情混沦言之则固有混然不可分开处。故各有所从来之说。果似微有未稳。而若人心道心则一生于形气。一原于性命。是非各有所从来而何。
老先生晚年之见
老先生之于四七论。虽有三两段因往复改其未安处。而其门户宗旨则非有初晚之别也。吾兄以此条为晚年定见。指甚条为初年未定之论耶。
大抵此卞差误处。专在于认人欲为人心。人欲之未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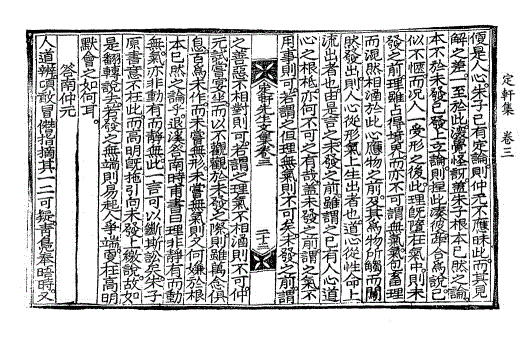 便是人心。朱子已有定论。则仲元不应昧此。而其见解之差。一至于此。深觉怪讶。盖朱子根本已然之论。本不于未发已发上立论。则捏此凑彼。牵合为说。已似不惬。而况人一受形之后。此理既堕在气中。则未发之前。理虽占得境界。而亦不可谓无气。气包畜理而混然相涵于此心应物之前。及其为物所触而闯然发出。则人心从形气上生出者也。道心从性命上流出者也。由是言之。未发之前。虽谓之已有人心道心之根柢。亦何不可之有哉。盖未发之前。谓之气不用事则可。若谓之但理无气则不可矣。未发之前。谓之善恶不相对则可。若谓之理气不相涵则不可。仲元试尝宴坐。而以不观观于未发之际。则虽万念俱息。百为未作。而未尝无形。未尝无气则又何嫌于根本已然之论乎。退溪答南时甫书曰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动有而静无。此一言可以断斯讼矣。朱子原书意不在此。而高明既拖引向未发上缴说。故如是翻转说去。若发之无端则易起人争端。更在高明默会之如何耳。
便是人心。朱子已有定论。则仲元不应昧此。而其见解之差。一至于此。深觉怪讶。盖朱子根本已然之论。本不于未发已发上立论。则捏此凑彼。牵合为说。已似不惬。而况人一受形之后。此理既堕在气中。则未发之前。理虽占得境界。而亦不可谓无气。气包畜理而混然相涵于此心应物之前。及其为物所触而闯然发出。则人心从形气上生出者也。道心从性命上流出者也。由是言之。未发之前。虽谓之已有人心道心之根柢。亦何不可之有哉。盖未发之前。谓之气不用事则可。若谓之但理无气则不可矣。未发之前。谓之善恶不相对则可。若谓之理气不相涵则不可。仲元试尝宴坐。而以不观观于未发之际。则虽万念俱息。百为未作。而未尝无形。未尝无气则又何嫌于根本已然之论乎。退溪答南时甫书曰理非静有而动无。气亦非动有而静无。此一言可以断斯讼矣。朱子原书意不在此。而高明既拖引向未发上缴说。故如是翻转说去。若发之无端则易起人争端。更在高明默会之如何耳。答南仲元
人道辨。顷敢冒僭指摘其一二可疑。青凫奉晤时。又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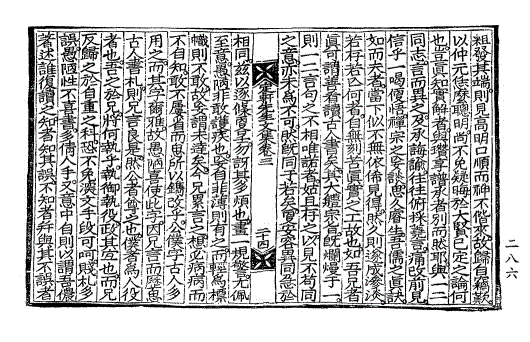 粗发其端。则见高明口顺而神不偕来。故归自窃叹。以仲元恁么聪明。尚不免疑晦于大贤已定之论何也。岂真知实解者。与瓒享谱承者别而然耶。与一二同志。言而异之。及承诲谕。往往俯采荛言。痛改前见。信乎一喝便悟。禅宗之妄谈。思久睿生。吾儒之真诀。如而夫者。当下似不无依俙见得。然久则遂成渗淡。若存若亡何者。自无刻苦真实之工故也。如吾兄者真可谓善看读古人书矣。其大体宗旨。既烂熳于一。则一二言句之不相唯诺者。姑且存之。以见不苟同之意。亦未为不可。然既同于若矣。更安容异同急于相同。玆以逐条更呈。勿讶其多烦也。画一规警。尤佩至意。愚陋非敢护疾也。妄自菲薄则有之。而轻为标帜则不敢。故妄谓未达矣。今兄累言之。想必病病而不自知。敢不屡省而思所以镌改乎。公仆字古人多用之。而其字尔雅。故愚陋喜使此字。因兄言而历思古人书札。则兄言良是。然公者尊之也。仆者为人役者也。吾之于兄。将何执乎。执御执役。政其宜也。而兄反归之于自重之科。恐不免深文手段可呵。贱札多误。愚陋性不喜书。多倩人手。又意中自则以谓吾侬著述谁复读之。知者知其误。不知者并与其不误者
粗发其端。则见高明口顺而神不偕来。故归自窃叹。以仲元恁么聪明。尚不免疑晦于大贤已定之论何也。岂真知实解者。与瓒享谱承者别而然耶。与一二同志。言而异之。及承诲谕。往往俯采荛言。痛改前见。信乎一喝便悟。禅宗之妄谈。思久睿生。吾儒之真诀。如而夫者。当下似不无依俙见得。然久则遂成渗淡。若存若亡何者。自无刻苦真实之工故也。如吾兄者真可谓善看读古人书矣。其大体宗旨。既烂熳于一。则一二言句之不相唯诺者。姑且存之。以见不苟同之意。亦未为不可。然既同于若矣。更安容异同急于相同。玆以逐条更呈。勿讶其多烦也。画一规警。尤佩至意。愚陋非敢护疾也。妄自菲薄则有之。而轻为标帜则不敢。故妄谓未达矣。今兄累言之。想必病病而不自知。敢不屡省而思所以镌改乎。公仆字古人多用之。而其字尔雅。故愚陋喜使此字。因兄言而历思古人书札。则兄言良是。然公者尊之也。仆者为人役者也。吾之于兄。将何执乎。执御执役。政其宜也。而兄反归之于自重之科。恐不免深文手段可呵。贱札多误。愚陋性不喜书。多倩人手。又意中自则以谓吾侬著述谁复读之。知者知其误。不知者并与其不误者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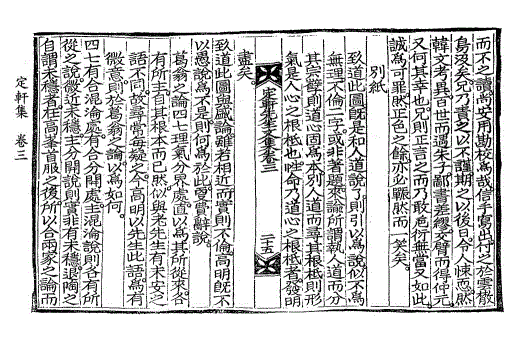 而不之读。尚安用勘校为哉。信手写出。付之于云散鸟没矣。兄乃责之以不谨。期之以后日。令人悚恧。然韩文考异。百世而遇朱子。鄙书差缪。交臂而得仲元。又何其幸也。兄则正言之而乃敢卮衍无当又如此。诚为可罪。然正色之馀。亦必辴然而一笑矣。
而不之读。尚安用勘校为哉。信手写出。付之于云散鸟没矣。兄乃责之以不谨。期之以后日。令人悚恧。然韩文考异。百世而遇朱子。鄙书差缪。交臂而得仲元。又何其幸也。兄则正言之而乃敢卮衍无当又如此。诚为可罪。然正色之馀。亦必辴然而一笑矣。别纸
致道此图既是和人道说了。则引以为说。似不为无理。不伦二字。或非著题。来谕所谓执人道而分其宗孽则道心固为本。别人道而寻其根柢则形气是人心之根柢也。性命乃道心之根柢者。发明尽矣。
致道此图。与盛论。虽若相近。而实则不伦。高明既不以愚说为不是。则何为于此。更费辞说。
葛翁之论四七理气分界处。直以为其所从来。各有所主。自其根本而已然。似与老先生有未安之语不同。故寻常每疑之。今高明以先生此语。为有微意。则于葛翁之论。以为如何。
四七有合混沦处。有合分开处。主混沦说则各有所从之说。微近未稳。主分开说则实非有未稳。退陶之自谓未稳者。在高峰首服之后。所以合两家之论而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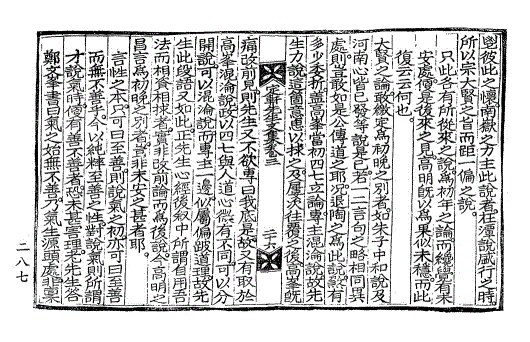 鬯彼此之怀。南岳之力主此说者。在潭说盛行之时。所以宗大贤之旨而距一偏之说。
鬯彼此之怀。南岳之力主此说者。在潭说盛行之时。所以宗大贤之旨而距一偏之说。只此各有所从来之说。为初年之论。而才觉有未安处。便是后来之见。高明既以为果似未稳。而此复云云何也。
大贤之论。敢缴定为初晚之别者。如朱子中和说及河南心皆已发等说是已。若一二言句之略相同异处。则岂敢如是公传道之耶。况退陶之为此说。煞有多少委折。盖高峰当初四七立论。专主混沦说。故先生力说这个意思以救之。及屡次往覆之后。高峰既痛改前见。则先生又不欲专曰我底是。故又有取于高峰混沦说。政以四七与人道心微有不同。可以分开说。可以混沦说。而专主一边。似属偏跛道理。故先生此段语又如此。正先生心经后叙中所谓自用吾法而相资相救者。实非改前论而为后说。今高明之昌言为初晚之别者。岂非未安之甚者耶。
言性之本。只可曰至善。则说气之初。亦可曰至善而无不善乎。今以纯粹至善之性。对说气则所谓才说气时。便有善不善者。恐未甚害理。老先生答郑文峰书曰气之始无不善。乃气生源头处。非禀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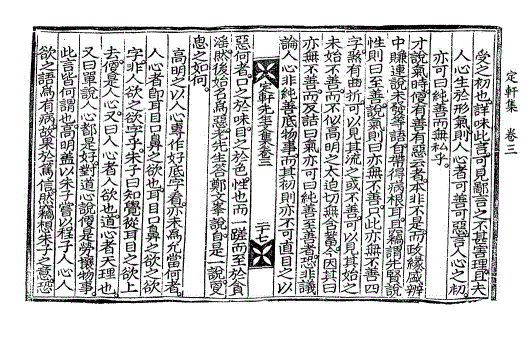 受之初也。详味此言。可见鄙言之不甚害理。且夫人心生于形气。则人心者可善可恶。言人心之初。亦可曰纯善而无私乎。
受之初也。详味此言。可见鄙言之不甚害理。且夫人心生于形气。则人心者可善可恶。言人心之初。亦可曰纯善而无私乎。才说气时。便有善有恶云者。本非不是。而政缘盛辨中赚连说未发等语。自带得病根耳。且窃谓先贤说性则曰至善。说气则曰亦无不善。只此亦无不善四字。煞有曲折。可以见其流之或不善。可以见其始之未始不善。而不似高明之太迫切无含蓄。今因其曰亦无不善。而反诘曰气亦可曰纯善至善者。恐非议论人心非纯善底物事。而其初则亦不可直目之以恶何者。口之于味。目之于色。性也而一蹉而至于贪淫。然后始名为恶。老先生答郑文峰说。自是一说。更思之如何。
高明之以人心专作好底字看。亦未为允当何者。人心者即耳目口鼻之欲也。耳目口鼻之欲之欲字。非人欲之欲字乎。朱子曰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又曰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又曰单说人心都是好。对道心说便是劳攘物事。此言皆何谓也。高明盖以朱子尝以程子人心人欲之语为有病。故果于笃信。然窃想朱子之意。恐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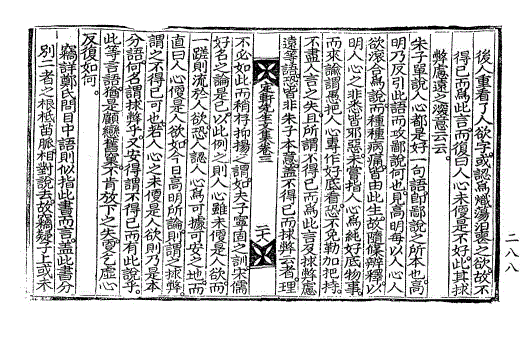 后人重看了人欲字。或认为炽荡汩丧之欲。故不得已而为此言。而复曰人心未便是不好。此其救弊虑远之深意云云。
后人重看了人欲字。或认为炽荡汩丧之欲。故不得已而为此言。而复曰人心未便是不好。此其救弊虑远之深意云云。朱子单说人心都是好一句语。即鄙说之所本也。高明乃反引此语而攻鄙说何也。见高明每以人心人欲滚合为说。而种种病痛。皆由此生。故随条辨释。以明人心之非悉皆邪恶。未尝指人心为纯好底物事。而来谕谓愚把人心专作好底看。恐不免勒加把持。不尽人言之失。且所谓不得已而为此言及救弊虑远等语。恐皆非朱子本意。盖不得已而救弊云者。理不必如此而稍存抑扬之谓。如夫子宁固之训。宋儒好名之论是已。以此例之则人心虽未便是人欲。而一蹉则流于人欲。恐人认人心为可据可安之地。而直曰人心便是人欲。如今日高明所论。则谓之救弊。谓之不得已可也。若人心之未便是人欲则乃是本分语。何名谓救弊乎。又安得谓不得已而有此说乎。此等言语。犹是顾恋旧窠。不肯放下之失。更乞虚心反复如何。
窃详郑氏问目中语则似指此书而言。盖此书分别二者之根柢苗脉。相对说去。故窃疑子上或未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9H 页
 免致疑于大本之相对而并立也。故当时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圣贤之言。各有地头。恐是一时矫偏救弊之论。似不可以此为不易之定论。而遽有所取舍也。来谕所谓必有加莹于此者。阔疏无情理。近于揣摸。恐非正意。
免致疑于大本之相对而并立也。故当时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圣贤之言。各有地头。恐是一时矫偏救弊之论。似不可以此为不易之定论。而遽有所取舍也。来谕所谓必有加莹于此者。阔疏无情理。近于揣摸。恐非正意。愚陋未尝敢辄生取舍于答郑蔡两书也。但以为与郑书中旨意。未必的指此书此条云耳。矫偏救弊之说。前段已尽之矣。加莹之云。虽近于无情意。而无情意中亦自有情意。所以明朱子此训至明至莹。无以复加之意。
未发之际。理气虽相涵。而理全而气偏。理正而气邪。这时节谓之理包蓄气则可。谓气包蓄理则理岂气之所包蓄者耶。恐偶失照管。
理虚气实。以气载理。如器贮水。器能贮水。水安能贮器乎。毋论未发已发。气能该载了理。而理不解包蓄得气。盖气属形器而理无作用故也。更思之如何。
答南仲元
秋间甥君袖记若书以来。而记则入手。书云漏失。殊觉缺甚。然大遁庵一记。吾仲元近日排置。纤悉无馀。书虽在又何以加焉。每暇时辄出山记。指点某曲可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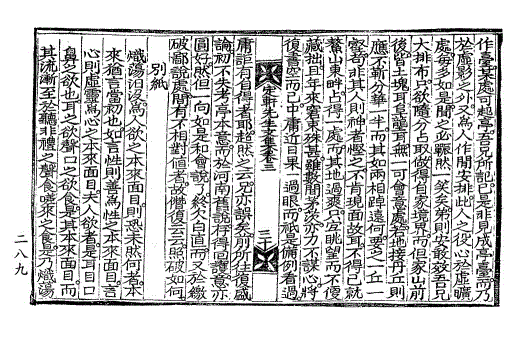 作台。某处可起亭。吾兄所记。已是非见成亭台。而乃于虚影之外。又为人作閒安排。此人之役心于虚旷处。每多如是。闻之必辴然一笑矣。弟则安敢效吾兄大排布。只欲随分占取。做得自家境界。而但家山前后。皆土块耳阜垄耳。无一可会意处。若地接丹丘则应不靳分华一半。而其如两相踔远何。要之一丘一壑。苟非其人则神者悭之。不肯现面故耳。不得已就鳌山东畔。占得一处。而其地过爽。只宜眺望而不便藏拙。且年来窘束殊甚。虽数间茅茨。亦力不谋心。将复书空而已。中庸近日果一过眼。而祇是备例看过。庸讵有自得者耶。超然之云。兄亦误矣。前所往复盛论。初不失考亭本意。而于河南旧说。存得回护。意亦圆好。然但一向如是和会说了。终欠白直。而又于缴破鄙说处。间有不相对值者。故僭复云云。照破如何。
作台。某处可起亭。吾兄所记。已是非见成亭台。而乃于虚影之外。又为人作閒安排。此人之役心于虚旷处。每多如是。闻之必辴然一笑矣。弟则安敢效吾兄大排布。只欲随分占取。做得自家境界。而但家山前后。皆土块耳阜垄耳。无一可会意处。若地接丹丘则应不靳分华一半。而其如两相踔远何。要之一丘一壑。苟非其人则神者悭之。不肯现面故耳。不得已就鳌山东畔。占得一处。而其地过爽。只宜眺望而不便藏拙。且年来窘束殊甚。虽数间茅茨。亦力不谋心。将复书空而已。中庸近日果一过眼。而祇是备例看过。庸讵有自得者耶。超然之云。兄亦误矣。前所往复盛论。初不失考亭本意。而于河南旧说。存得回护。意亦圆好。然但一向如是和会说了。终欠白直。而又于缴破鄙说处。间有不相对值者。故僭复云云。照破如何。别纸
炽荡汩没。为人欲之本来面目。则恐未然何者。本来犹言当初也。如言性则善为性之本来面目。言心则虚灵为心之本来面目。夫人欲者。是耳目口鼻之欲也。耳之欲声口之欲食。是其本来面目。而其流渐至于听非礼之声食嗟来之食。是乃炽荡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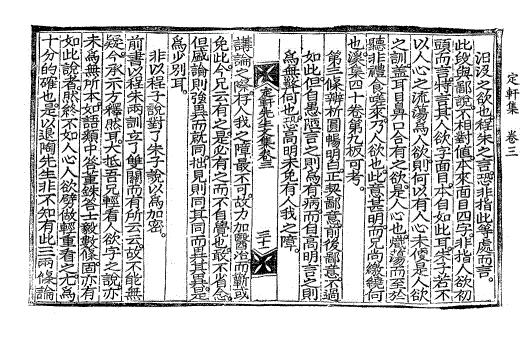 汩没之欲也。程朱之言。恐非指此等处而言。
汩没之欲也。程朱之言。恐非指此等处而言。此段与鄙说。不相对值。本来面目四字。非指人欲初头而言。特言其人欲字面目。本自如此耳。朱子若不以人心之流荡为人欲。则何以有人心未便是人欲之训。盖耳目鼻口合有之欲。是人心也。炽荡而至于听非礼食嗟来。乃人欲也。此意甚明。而兄尚缴绕何也。溪集四十卷第九板可考。
第三条辨析圆畅明白。正契鄙意。前后鄙意。不过如此。但自愚陋言之则为有病。而自高明言之则为无弊何也。恐高明未免有人我之障。
讲论之际。存人我之障最不可。故力加医治。而蕲或免此。今兄云有之。是必有之而不自觉也。敢不省念。但盛论则强异而就同。拙见则同其同而异其异。是为少别耳。
非以程子说对了朱子说以为加密。
前书以程朱两训立了双关而有所云云。故不能无疑。今承示方释然耳。大抵吾兄轻看人欲字之说。亦未为无所本。如语类中答董铢答士毅数条。固亦有如此说者。然终不如人心人欲劈做轻重看之。尤为十分的确也。是以退陶先生非不知有此三两条论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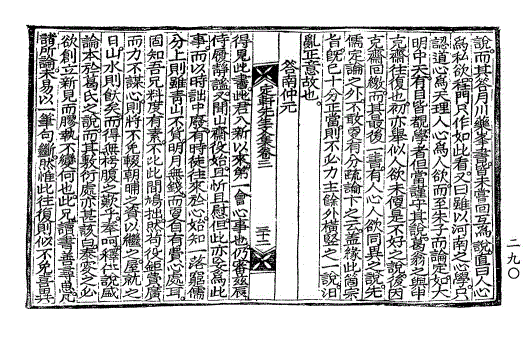 说。而其答月川药峰书。皆未尝回互为说。直曰人心为私欲。程门只作如此看。又曰虽以河南之心学。只认道心为天理人心为人欲。而至朱子而论定。如大明中天。有目皆睹。学者但当谨守其说。葛翁之与申克斋往复也。初亦举似人欲未便是不好之说。后因克斋回缴。而其最后一书。有人心人欲同异之说。先儒定论之外。不敢更有分疏论卞之云。盖缘此个宗旨。既已十分正当。则不必力主馀外横竖之一说。汩乱正意故也。
说。而其答月川药峰书。皆未尝回互为说。直曰人心为私欲。程门只作如此看。又曰虽以河南之心学。只认道心为天理人心为人欲。而至朱子而论定。如大明中天。有目皆睹。学者但当谨守其说。葛翁之与申克斋往复也。初亦举似人欲未便是不好之说。后因克斋回缴。而其最后一书。有人心人欲同异之说。先儒定论之外。不敢更有分疏论卞之云。盖缘此个宗旨。既已十分正当。则不必力主馀外横竖之一说。汩乱正意故也。答南仲元
得见此书。此君入新以来。第一会心事也。仍审玆辰。侍履静谧。又闻山斋役始。且忻且慰。但此亦妄为此事。而以时诎中废。有时徒往来于心。始知一落穷儒分上则虽青山不货。明月无钱。而更自有费心处耳。固知吾兄料度有素。不比此间鸠拙。然苟役钜费广而力不谋心。则将不免辍朝晡之资以继之。屋就之日。山水则饫矣。而得无枵腹之叹乎。奉呵。释仁说盛论本于葛氏之说。而其敷衍处亦甚该白。泰叟之必欲创立新见而胶执不变何也。此兄读书善寻思。凡诸所论。未易以一笔句断。然惟此往复则似不免喜异
定轩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291H 页
 之病。更叩之如何。或恐一时意见。未及契勘故耳。但兄书中一二语句。亦似有合商处。岂笔快耶。如以心之德为仁字本训者。恐似非朱子论仁本意。盖偏言全言。虽有偏全之不同。然仁字真面目则正在偏言处。更入思议焉。
之病。更叩之如何。或恐一时意见。未及契勘故耳。但兄书中一二语句。亦似有合商处。岂笔快耶。如以心之德为仁字本训者。恐似非朱子论仁本意。盖偏言全言。虽有偏全之不同。然仁字真面目则正在偏言处。更入思议焉。与韩参判(镇庭)
进昵声光。殆且十载。区区识荆。虽窃自幸。而第未知吾閤下尚能收置意中否耳。间尝有造候之便。而窃闻明公时望方隆。遂不敢破宿戒而归。然当海内眇然之时。閤下屹然为吾党之领袖。使一队士流有所恃而不恐。虽潜深伏隩。昧昧如鲰生者。曷尝忘慕庸之勤哉。伏惟郊凉。台体动止候若序崇护。钟祥病伏穷海。不烦人弃而己甘自弃。惟愿耕田种黍。勤身节用。以为事亲供宾之须。间与一二弟侄辈。讨坟谈典。度了时日。而此外实无毫发馀念。其所可欲者。亦廉矣。而天又靳之。顷年哭妻。身世悲凉。馀外功衰之戚。又相随属。自遣之道。惟在习忘二字。而习之之久。遂成閒懒。并与不可废之旧业而废之。四十无闻。亦云其终。而居已四十而一矣。静自循省。时一喟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