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书
书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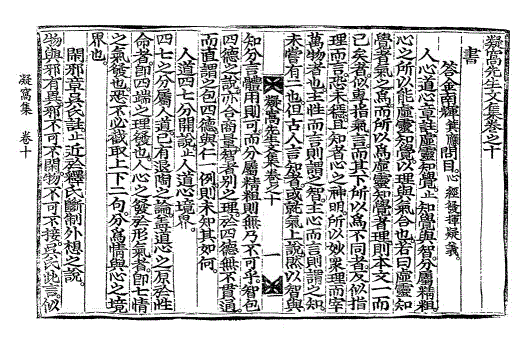 答金南辉(箕应)问目。(心经发挥疑义。)
答金南辉(箕应)问目。(心经发挥疑义。)人心道心章注。虚灵知觉。(止。)知觉与智。分属精粗。
心之所以能虚灵知觉。以理与气合也。若曰虚灵知觉者气之为。而所以为虚灵知觉者理。则本文一而已矣者。似专指气言。而其下所以为不同者。反似指理而言。恐未稳。且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主性而言则谓之智。主心而言则谓之知。未尝有二也。但古人言知者。或就气上说。然以智与知分言体用则可。而分属精粗则无乃不可乎。智包四德之说。亦合商量。智者别之理。于四德无不贯通。而直谓之包四德。与仁一例。则未知其如何。
人道四七分开说。(止。)人道心境界。
四七之分属人道。已有退陶之论。盖道心之原于性命者。即四端之理发也。人心之发于形气者。即七情之气发也。恐不必截取上下二句。分为情与心之境界也。
闲邪章吴氏注。(止。)近于释氏断制外想之说。
物与邪有异。邪不可不闲。物不可不接。吴氏此言。似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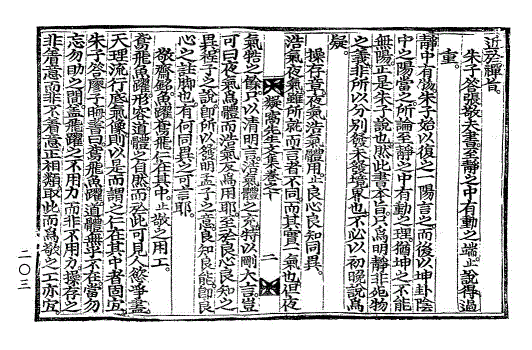 近于禅旨。
近于禅旨。朱子答张敬夫书。至静之中有动之端。(止。)说得过重。
静中有物。朱子始以复之一阳言之。而后以坤卦阴中之阳当之。所论至静之中有动之理。犹坤之不能无阳。正是朱子说也。然此书本旨。只为明静非死物之义。非所以分别发未发境界也。不必以初晚说为疑。
操存章。夜气浩气体用。(止。)良心良知同异。
浩气夜气。虽所就而言者不同。而其实一气也。但夜气牿之馀。只以清明言。浩气体之充。特以刚大言。岂可曰夜气为体而浩气反为用耶。至于良心良知之异。程子之说。即所以发明孟子之意。良知良能。即良心之注脚也。有何同异之可言耶。
敬斋铭。鱼跃鸢飞仁在其中。(止。)敬之用工。
鸢飞鱼跃。形容道体之自然。而于此可见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底气像。则以是而谓之仁在其中者固宜。朱子答廖子晦书曰。鸢飞鱼跃。道体无乎不在。当勿忘勿助之间。盖飞跃之不用力而非不用力。操存之非着意而非不着意正相类。取此而为敬之工亦宜。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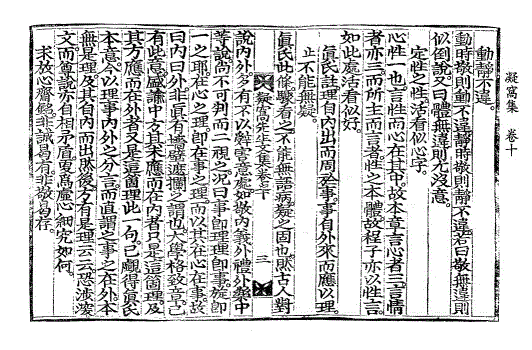 动静不违。
动静不违。动时敬则动不违。静时敬则静不违。若曰敬无违则似倒说。又曰体无违则尤没意。
定性之性。活看似心字。
心性一也。言性而心在其中。故本章言心者三。言情者亦三。而所主而言者。性之本体。故程子亦以性言。如此处活看似好。
真氏注。理自内出而周于事。事自外来而应以理。(止。)不能无疑。
真氏此条。骤看之。不能无语病。疑之固也。然古人对说内外。多有不以辞害意处。如敬内义外礼外乐中等说。尚不可判而二视之。况曰事即理理即事。旋即一之耶。在心之理。即在事之理。而以其在心在事。故曰内曰外。非真有墙壁遮拦之谓也。大学格致章。已有此意。盛谕中方其未应而在内者只是这个理。及其方应而在外者又是这个理此一句。已觑得真氏本意。今以理事内外之分言。而直谓之事之在外。本无是理。及其自内而出然后。方有是理云云。恐涉深文。而尊说亦自相矛盾。更为虚心细究如何。
求放心斋铭。非诚曷有。非敬曷存。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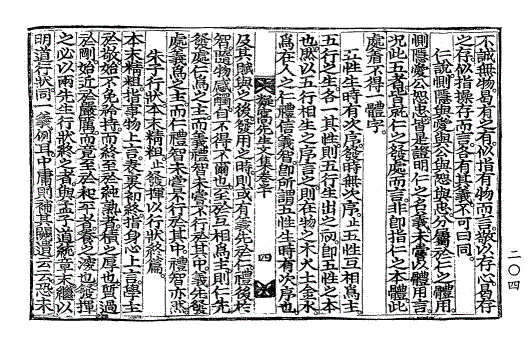 不诚无物。曷有之有。似指有物而言。敬以存心。曷存之存。似指操存而言。各有其义。不可曰同。
不诚无物。曷有之有。似指有物而言。敬以存心。曷存之存。似指操存而言。各有其义。不可曰同。仁说。恻隐与爱与公与恕与忠。分属于仁之体用。
恻隐爱公恕忠。皆是證明仁之名义。未尝以体用言。况此五者。皆就仁之发处而言。非即指仁之本体。此处着不得一体字。
五性生时有次序。发时无次序。(止。)五性互相为主。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则五行生出之初。即五性之本也。然以五行相生之序言之。则在物之木火土金水。为在人之仁礼信义智。即所谓五性生时有次序也。及其赋与之后。发用之时。则或有义先于仁。礼后于智。随物感触。自不得不尔也。至于互相为主。则仁先发处仁为之主。而义礼智未尝不行于其中。义先发处义为之主。而仁礼智未尝不行于其中。礼智亦然。
朱子行状。本末精粗。(止。)发挥以行状终篇。
本末精粗。指事物上言。表里初终。指身心上言。学主于敬。始不免矜持。而终至于纯熟者。积之厚也。质过于刚。始近于严厉。而竟至于和平者。养之深也。发挥之必以两先生行状终之者。与孟子道统章末。继以明道行状。同一义例耳。中庸则补其阙遗云云。恐未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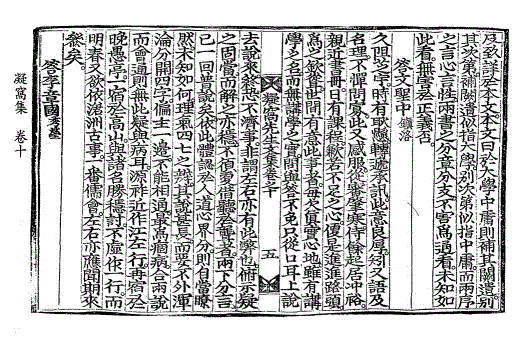 及致详于本文。本文曰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补阙遗似指大学。别次第似指中庸。而两序之言心言性。两书之分章分支。不害为通看。未知如此看。无害于正义否。
及致详于本文。本文曰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补阙遗似指大学。别次第似指中庸。而两序之言心言性。两书之分章分支。不害为通看。未知如此看。无害于正义否。答文圣中(镇洛)
久阻芝宇。时有耿悬。转递承讯。此意良厚。矧又语及名理。不惮问寡。此又感服。从审肇寒。侍馀起居冲裕。亲近书册。日有课程。歉若不足之心。便是进进路头。为之钦耸。世间有意此事者。每欠真实心地。虽有讲学之名。而无讲学之实。问与答不免只从口耳上说去说来。终恐不济事。非谓左右亦有此弊也。俯示疑之固当。而解之亦稳。不须更借听于聋者。两下分言。已一回普说矣。依此体认于人道心界分。则自当瞭然。未知如何。理气四七之辨。其说甚长。而要不外浑沦分开四字。偏主一边。不能相通。最为痼病。合两说而会通则无此疑与病耳。源祚近作江左行。再宿于晚愚亭。一宿于高山。与诸名胜稳讨。不虚作一行。而明春又欲依沧洲古事。一番儒会。左右亦应闻期来参矣。
答李章国(秀莹)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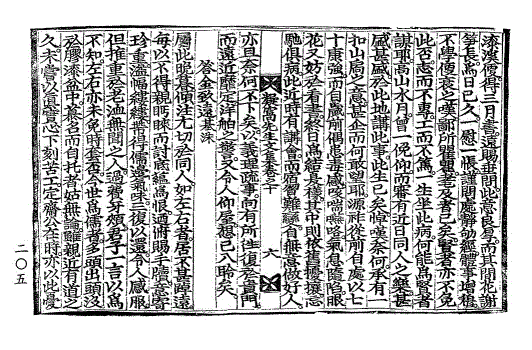 漆溪便。得三月书。远赐垂问。此意良厚。而其间花谢笋长。为日已久。一慰一怅。谨问处静劬经。体事增穆。不学便衰之叹。鄙所瞿瞿。耄及者已矣。贤者亦不免此否。志而不专。工而不笃。一生坐此病。何能为贤者谋耶。高山水月。曾一俛仰。而审有近日同人之乐。甚盛甚盛。于此地讲此事。此生已矣。悼叹奈何。承有一扣山扃之意。甚企而何敢望耶。源祚从前自处以七十康强。而自岁前偶患毒感。咳喘咽咯。气息随陷。眼花又妨于看书。终日为结夏样。其中则依旧扰攘。忘驰俱病。此近时有讲会。而宿习难变。自无意做好人。亦且奈何不下矣。以义理疏事。向有所往复于贵门。而远近靡定。洋舶之警。又令人仰屋。想已入聆矣。
漆溪便。得三月书。远赐垂问。此意良厚。而其间花谢笋长。为日已久。一慰一怅。谨问处静劬经。体事增穆。不学便衰之叹。鄙所瞿瞿。耄及者已矣。贤者亦不免此否。志而不专。工而不笃。一生坐此病。何能为贤者谋耶。高山水月。曾一俛仰。而审有近日同人之乐。甚盛甚盛。于此地讲此事。此生已矣。悼叹奈何。承有一扣山扃之意。甚企而何敢望耶。源祚从前自处以七十康强。而自岁前偶患毒感。咳喘咽咯。气息随陷。眼花又妨于看书。终日为结夏样。其中则依旧扰攘。忘驰俱病。此近时有讲会。而宿习难变。自无意做好人。亦且奈何不下矣。以义理疏事。向有所往复于贵门。而远近靡定。洋舶之警。又令人仰屋。想已入聆矣。答金致远(基洙)
属此晚暮。倾注尤切于同人。如左右者。居不甚踔远。每以不得亲眄睐而讨底蕴为恨。乃俯赐手牍。意寄珍重。溢幅缕缕。带得儒边气味。三复以还。令人感服。但推重于老洫无闻之人。过费牙颊。君子一言以为不知。左右亦未免时套否。今世为儒者。多头出头没于胶漆盆中。慕名而自托者姑无论。虽亲近有道之久。未尝以真实心下刻苦工。定斋公在时。亦以此忧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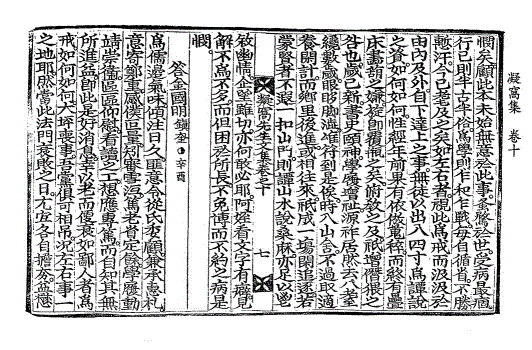 悯矣。顾此本未始无意于此事。蚤骛于世。受病最痼。行己则半古半俗。为学则乍和乍战。每自循省。不胜惭汗。今已耄及之矣。如左右者。视此为戒而汲汲于由内及外。自下达上之事。无徒以出入四寸为谭说之资。如何如何。性经年前果有依仿蒐稡。而终有叠床画葫之嫌。旋即覆瓶之矣。俯教之及。祇增僭猥之咎也。岁已新。书史颐神。学履增祉。源祚居然去八耋才数岁。眼眵脚涩。唯符到是俟。时入山舍。不过取适养闲计。而乡里后进。或相往来。祇成一场闲追逐。若蒙贤者不遐一扣山门。则谭山水说桑麻。亦足以鬯叙幽情。企望虽切。亦何敢必耶。阿侄看文字有癖。见解不为不多。而但困于所长。不免博而不约之病是悯。
悯矣。顾此本未始无意于此事。蚤骛于世。受病最痼。行己则半古半俗。为学则乍和乍战。每自循省。不胜惭汗。今已耄及之矣。如左右者。视此为戒而汲汲于由内及外。自下达上之事。无徒以出入四寸为谭说之资。如何如何。性经年前果有依仿蒐稡。而终有叠床画葫之嫌。旋即覆瓶之矣。俯教之及。祇增僭猥之咎也。岁已新。书史颐神。学履增祉。源祚居然去八耋才数岁。眼眵脚涩。唯符到是俟。时入山舍。不过取适养闲计。而乡里后进。或相往来。祇成一场闲追逐。若蒙贤者不遐一扣山门。则谭山水说桑麻。亦足以鬯叙幽情。企望虽切。亦何敢必耶。阿侄看文字有癖。见解不为不多。而但困于所长。不免博而不约之病是悯。答金国明(镇奎○辛酉)
为儒边气味。倾注日久。匪意令从氏委顾。兼承惠札。意寄郑重。感仆叵量。矧审雪冱。笃老省定馀。学履动靖崇卫。区区仰慰。看读之工。想应专笃。而自知其无所进益。即此是好消息。幸以老而便衰如鄙人者为戒。如何如何。大坪丧事。吾党俱可相吊。况左右事一之地耶。然当此法门衰败之日。尤宜各自担夯。益懋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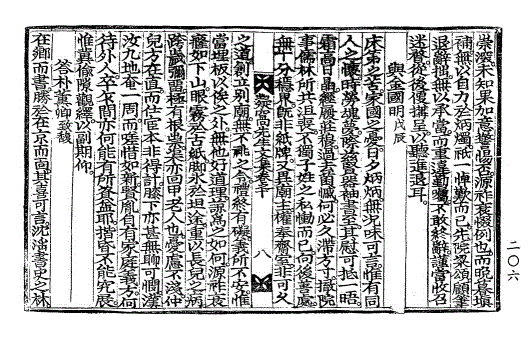 崇深。未知果加意警惕否。源祚衰惙例也。而晚暮填补。无以自力于炳烛。祇一悼叹而已。先院梁颂。顾笔退辞拙。无以承当。而重违勤嘱。不敢终辞。谨当收召迷瞀。从后便搆呈。以听进退耳。
崇深。未知果加意警惕否。源祚衰惙例也。而晚暮填补。无以自力于炳烛。祇一悼叹而已。先院梁颂。顾笔退辞拙。无以承当。而重违勤嘱。不敢终辞。谨当收召迷瞀。从后便搆呈。以听进退耳。与金国明(戊辰)
床笫之苦。家国之忧。日夕炳炳。无况味可言。惟有同人之怀。时劳魂梦。际玆贤器袖书至。其慰可抵一晤。霜高日晶。经履庄穆。过去菌戚。何必久滞方寸。撤院事儒林所共沮丧。不独子姓之私恸而已。向后善处。无十分稳界。既非纸牌。又异庙主。权奉斋室。非可久之道。创立别庙。无不祧之令。礼终有碍。义所不安。惟当埋板以俟之外。无他好道理。谅为之如何。源祚衰癃如下山。眼雾于古纸。脚冰于坦途。重以长儿之病。跨岁弥留。极有根祟。渠亦回甲老人也。忧虑不浅。仲儿方在直。而仕宦本非得计。膝下亦甚无聊可悯。汉汝九地奄一周。而嗟惜如新。贤胤自有家庭义方。何待外人。卒乍间亦何能有所资益耶。揩昏不能究展。惟冀偷隙观绎。以副期仰。
答朴薰卿(致馥)
在乡而书。胜于在京而面。其喜可言。沈淫书史之林。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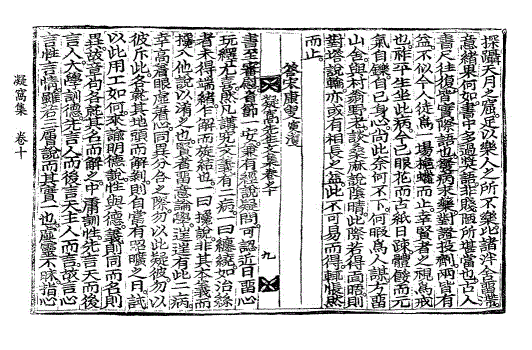 探蹑天月之窟。足以乐人之所不乐。比诸泮舍留滞。意绪果何如。书中多过奖语。非贱陋所堪当也。古人书尺往复。皆实际语也。发病求药。对證投剂。两皆有益。不似今人徒为一场栀蜡而止。幸贤者之视为戒也。祚平生坐此病。今已眼花而古纸日疏。体馁而元气自铄。自己身心。尚此奈何不下。何暇为人谋。方留山舍。与村翁野老。谈桑麻说阴晴。此际若得面晤。则对塔说轮。亦或有相长之益。此不可易而得。辄怅然而止。
探蹑天月之窟。足以乐人之所不乐。比诸泮舍留滞。意绪果何如。书中多过奖语。非贱陋所堪当也。古人书尺往复。皆实际语也。发病求药。对證投剂。两皆有益。不似今人徒为一场栀蜡而止。幸贤者之视为戒也。祚平生坐此病。今已眼花而古纸日疏。体馁而元气自铄。自己身心。尚此奈何不下。何暇为人谋。方留山舍。与村翁野老。谈桑麻说阴晴。此际若得面晤。则对塔说轮。亦或有相长之益。此不可易而得。辄怅然而止。答宋康叟(寅濩)
书至审慰。省节一安。兼有经说疑问。可认近日留心玩绎尤喜。然凡讲究文义有二病。一曰缠绕。如治丝者未得端绪。乍解而旋结也。一曰搀说。非其本义而搀入他说以淆之也。贤者留意论学。𨓏𨓏有此二病。幸高着眼虚着心。同异分合之际。勿以此疑彼。勿以彼斥此。各就其地头而解剥。则自当有昭旷之日。试以此用工如何。来谕明德说。性与德。义则同而名则异。故章句各就其名而解之。中庸训性。先言天而后言人。大学训德。先言人而后言天。主人而言。故言心言性言情。虽若三层说而其实一也。虚灵不昧。指心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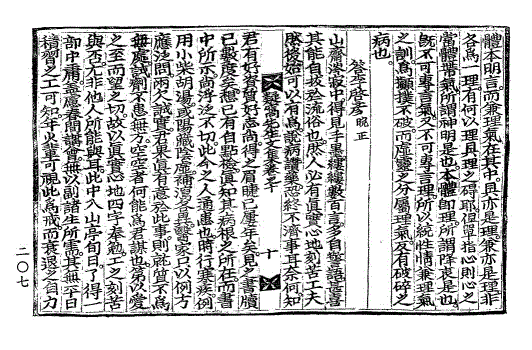 体本明言。而兼理气在其中。具亦是理。兼亦是理。非各为一理。有何以理具理之碍耶。但单指心则心之当体带气。所谓神明是也。本体即理。所谓降衷是也。既不可专言气。又不可专言理。所以统性情兼理气之训。为攧扑不破。而虚灵之分属理气。反有破碎之病也。
体本明言。而兼理气在其中。具亦是理。兼亦是理。非各为一理。有何以理具理之碍耶。但单指心则心之当体带气。所谓神明是也。本体即理。所谓降衷是也。既不可专言气。又不可专言理。所以统性情兼理气之训。为攧扑不破。而虚灵之分属理气。反有破碎之病也。答李启彦(晚正)
山斋涔寂中。得见手墨。缕缕数百言。多自警语。甚喜其能自拔于流俗也。然人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然后。始可以有为。说病赞药。恐终不济事耳奈何。知君有好资质好志尚。得之眉睫已屡年矣。见之书牍已数度矣。想已有自点检。真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书中所示。尚浮泛不切。此今之人通患也。时行寒疾。例用小柴胡汤。或阳藏阴虚。补泻各异。医家只以例方应泛问。两欠诚实。君果真有意于此事。则就质不为无处。试剂不患无方。空空者何能为君谋也。第以爱之至而望之切。故以真实心地四字奉勉。工之刻苦与否。尤非他人所能与耳。此中入山亭旬日。了得一部中庸。盖虑春间讲会。无以副诸生所需。其无平日积习之工可知。年少辈可视此为戒。而衰退之自力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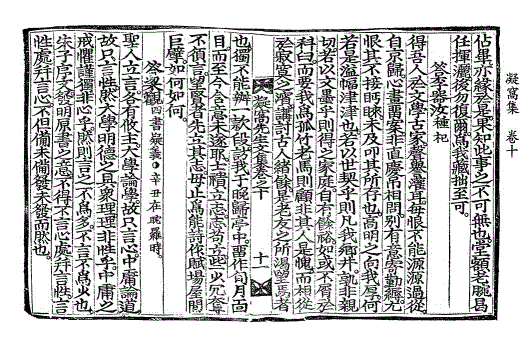 佔毕。亦缘于是。果知此事之不可无也。堂额老腕曷任挥洒。后勿复尔。为我藏拙至可。
佔毕。亦缘于是。果知此事之不可无也。堂额老腕曷任挥洒。后勿复尔。为我藏拙至可。答李器汝(种杞)
得吾人于文学古家。声誉灌耳。每恨不能源源过从。自京归。心画留案。非直庆吊相问。别有意寄勤缛。尤恨其不接眄睐。未及叩其所存也。高明之向我厚。何若是溢幅津津也。若以世契乎则凡我乡井。孰非亲切。若以文墨乎则得之家庭。自有馀裕。如或不屑于科臼。而要我为孤竹老马则顾非其人是愧。而相从于寂寞之滨。讲讨古人绪馀。是老友之所渴望焉者也。独不能办一款段。访我于晚归亭中。留作旬月面目。而至今含意未遂耶。士贵立志。志苟立。些少冗夺不须言。望贤者先立其志。毋止为能诗作赋场屋间巨擘。如何如何。
答梁观(四书疑义○辛丑在耽罗时)
圣人立言。各有攸主。大学论学。故只言心。中庸论道。故只言性。然大学明德之具众理。理非性乎。中庸之戒惧谨独非心乎。然则言之不为多。不言不为少也。朱子序文。发明原书之意。不得不言心处并言性。言性处并言心。不但备未备发未发而然也。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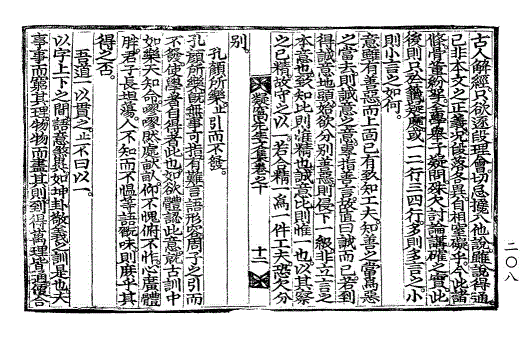 古人解经。只欲逐段理会。切忌搀入他说。虽说得通。已非本文之正义。况段落各异。自相窒碍乎。今此诸条。骨董纷挐。全学举子疑问。殊欠讨论讲确之实。此后则只于签疑处。或一二行三四行。多则多言之。小则小言之如何。
古人解经。只欲逐段理会。切忌搀入他说。虽说得通。已非本文之正义。况段落各异。自相窒碍乎。今此诸条。骨董纷挐。全学举子疑问。殊欠讨论讲确之实。此后则只于签疑处。或一二行三四行。多则多言之。小则小言之如何。意虽有善恶。而上面已有致知工夫。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则诚意之意。专指善言。故直曰诚而已。若到得诚意地头。始欲分别善恶。则侵下一级。非立言之本意也。致知比则惟精也。诚意比则惟一也。以其察之已精。故守之以一。若合精一为一件工夫。恐欠分别。
孔颜所乐。(止。)引而不发。
孔颜所乐。既无事可指。有难言语形容。周子之引而不发。使学者自得者此也。如欲体认此意。就古训中如乐天知命。嘐嘐然处𤱶亩。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君子长坦荡。人不知而不愠等语玩味。则庶乎其得之否。
吾道一以贯之。(止。)不曰以一。
以字上下之间。语意煞异。如坤卦敬义之训是也。夫事事而穷其理。物物而尽其则。到得万理皆通。便合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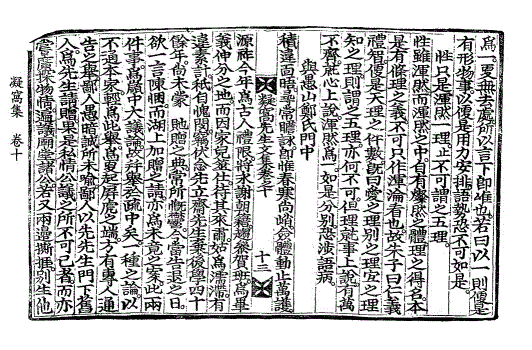 为一。更无去处。所以言下即唯也。若曰以一则便是有形物事。以便是用力安排。语势恐不可如是。
为一。更无去处。所以言下即唯也。若曰以一则便是有形物事。以便是用力安排。语势恐不可如是。性只是浑然一理。(止。)不可谓之五理。
性虽浑然。而浑然之中。自有灿然之体。理之得名。本是有条理之义。不可只作浑沦看也。故朱子曰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既曰爱之理别之理宜之理知之理。则谓之五理。亦何不可。但理就事上说。有万不齐。就心上说。浑然为一。如是分别。恐涉语病。
与愚山郑氏门中
积违面晤。寻常瞻咏。即惟春寒尚峭。佥体动止万护。源祚今年为古人礼限。将永谢朝籍。趋参贺班。为毕义伸分之地。而因家儿筮仕。待其来肃。姑为濡滞。有违素计。秖自愧闵。窃伏念先立斋先生弃后学四十馀年。尚未蒙 貤赠之典。常所慨郁。今当告退之日。欲一言陈悃。而湖上加赠之请。亦为未竟之案。此两件事。为岭中大议论。故并举于疏中矣。一种之论。以不通本家。轻为此举。为更起屏虎之端。方有专人通告之举。鄙人愚暗诚所未喻。鄙人以先先生门下旧人。为先生请赠。果是私情公议之所不可已者。而亦尝广探物情。遍议庙堂诸公。若又两边撕挨。别生他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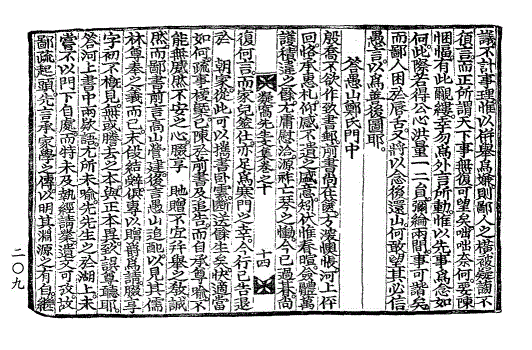 议。不计事理。惟以并举为嫌。则鄙人之横被疑谤不须言。而正所谓天下事无复可望矣。咄咄奈何。要陈悃愊。有此覼缕。幸勿为外言所动。惟以先事为念如何。此际若得公心洪量一二员。弥纶两间。事可谐矣。而鄙人困于唇舌。又将以念后还山。何敢望其必信愚言。以为善后图耶。
议。不计事理。惟以并举为嫌。则鄙人之横被疑谤不须言。而正所谓天下事无复可望矣。咄咄奈何。要陈悃愊。有此覼缕。幸勿为外言所动。惟以先事为念如何。此际若得公心洪量一二员。弥纶两间。事可谐矣。而鄙人困于唇舌。又将以念后还山。何敢望其必信愚言。以为善后图耶。答愚山郑氏门中
殷乔不欲作致书邮。前书尚在箧。方深懊怅。河上伻回。恪承惠札。仰感不遗之盛意。矧伏惟春暄。佥体万护。积违之馀。尤庸慰洽。源祚亡琴之恸。今已过期。尚复何言。而家儿筮仕。亦足为寒门之幸。今行已告退于 朝家。从此可以携书卧云。断送馀生矣。快适当如何。疏事梗槩。已陈于前书及追告。而自承尊喻。不能无蹙然不安之心。啜享 貤赠不宜并举之教诚然。而鄙书前言高山营建。后言愚山追配。以见其儒林尊奉之义而已。末段结辞。俱专以赠爵为请。啜享字初不概见。无或誊去之本。与正本异。致误尊听耶。答河上书中两款语。尤所未喻。先先生之于湖上。未尝不以门下自处。而特未及执经请业。遗文可考。故鄙疏起头。先言承家学之传。以明其渊源之有自。继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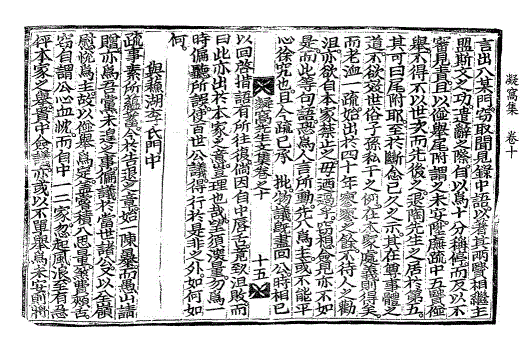 言出入某门。窃取闻见录中语。以著其两贤相继主盟斯文之功。遣辞之际。自以为十分称停。而反以不审见责。且以并举尾附谓之未安。升庑疏中五贤并举。不得不以世次而先后之。退陶先生之居于第五。其可曰尾附耶。至于断念已久之示。其在尊事体之道。不欲效世俗子孙私干之例。在本家处义则得矣。而老洫一疏。始出于四十年寥寥之馀。不待人之劝沮。亦欲自本家禁止之。毋乃过乎。窃想佥见亦不如是。而此等句语。恐为人言所动。先入为主。或不能平心徐究也。且今疏已承 批。物议既尽回公。时相已以回启措语有所往复。倘因自中唇舌。竟致沮败。而曰此亦出于本家之意。岂理也哉。望须深量。勿为一时偏听所误。使百世公议。得行于是非之外。如何如何。
言出入某门。窃取闻见录中语。以著其两贤相继主盟斯文之功。遣辞之际。自以为十分称停。而反以不审见责。且以并举尾附谓之未安。升庑疏中五贤并举。不得不以世次而先后之。退陶先生之居于第五。其可曰尾附耶。至于断念已久之示。其在尊事体之道。不欲效世俗子孙私干之例。在本家处义则得矣。而老洫一疏。始出于四十年寥寥之馀。不待人之劝沮。亦欲自本家禁止之。毋乃过乎。窃想佥见亦不如是。而此等句语。恐为人言所动。先入为主。或不能平心徐究也。且今疏已承 批。物议既尽回公。时相已以回启措语有所往复。倘因自中唇舌。竟致沮败。而曰此亦出于本家之意。岂理也哉。望须深量。勿为一时偏听所误。使百世公议。得行于是非之外。如何如何。与苏湖李氏门中
疏事素所蕴蓄。今于告退之章。始一陈㬥。而愚山请赠。亦为吾党未遑之事。遍议于当世诸公。又以全岭慰悦为主。故以并举为定。盖尝积入思量。煞费颊舌。窃自谓公心血忱。而自中一二家。忽起风浪。至有急伻本家之举。贵中佥议。亦或以不单举为未安则将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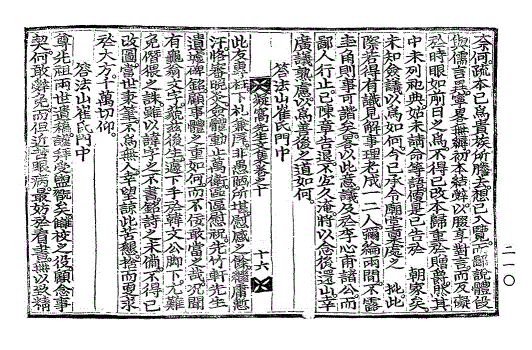 奈何。疏本已为贵族所誊去。想已入览。而鄙说体段与儒言异。宁略无缛。初本结辞。以啜享对言。而反碍于时眼如前日之为。不得已改本归重于赠爵。然其中未列祀典。姑未请命等语。便是已告于 朝家矣。未知佥议以为如何。今已承令庙堂禀处之 批。此际若得有识见解事理老成一二人。弥纶两间。不露圭角则事可谐矣。略以此意。议及于李心甫诸公。而鄙人行止。已陈章告退。不宜久淹。将以念后还山。幸广议熟虑。以为善后之道如何。
奈何。疏本已为贵族所誊去。想已入览。而鄙说体段与儒言异。宁略无缛。初本结辞。以啜享对言。而反碍于时眼如前日之为。不得已改本归重于赠爵。然其中未列祀典。姑未请命等语。便是已告于 朝家矣。未知佥议以为如何。今已承令庙堂禀处之 批。此际若得有识见解事理老成一二人。弥纶两间。不露圭角则事可谐矣。略以此意。议及于李心甫诸公。而鄙人行止。已陈章告退。不宜久淹。将以念后还山。幸广议熟虑。以为善后之道如何。答法山崔氏门中
此友专枉。下札兼辱。非愚陋所堪。慰感之馀。继庸惭汗。恪审晚炎。佥体动止万卫。区区慰祝。先竹轩先生遗墟碑铭。顾事体之重如何。而不佞敢当之哉。况闻有龟翁文字。藐玆后生。遽下手于韩文公脚下。尤难免僭猥之诛。虽以讳字之不书。铭诗之未备。不得已改图。当世秉笔。不为无人。幸望谅此苦恳。舍而更求于大方。千万切仰。
答法山崔氏门中
尊先祖两世遗稿。谨拜受盥玩矣。雠校之役。顾念事契。何敢辞免。而但近苦眼病。最妨于看书。无以致精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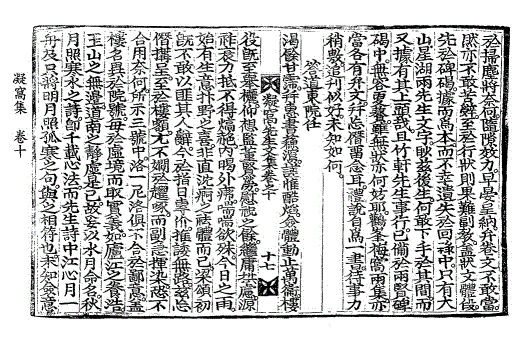 于扫尘将奈何。随隙效力。早晏呈纳。弁卷文不敢当。然亦不敢苦辞。至于行状则果难副教。盖状文体段。先于碑碣。据而为本。而不幸遗失于回禄中。只有大山,星湖两先生文字。眇玆后生。何敢下手于其间。而又据有其上头哉。且竹轩先生事行。已备于两贤碑碣中。无容更赘。虽无状亦何妨耶。鹳峰,梅窝两集。亦当各有弁文。并忘僭留念耳。礼说自为一书。待事力稍敷。追刊似好。未知如何。
于扫尘将奈何。随隙效力。早晏呈纳。弁卷文不敢当。然亦不敢苦辞。至于行状则果难副教。盖状文体段。先于碑碣。据而为本。而不幸遗失于回禄中。只有大山,星湖两先生文字。眇玆后生。何敢下手于其间。而又据有其上头哉。且竹轩先生事行。已备于两贤碑碣中。无容更赘。虽无状亦何妨耶。鹳峰,梅窝两集。亦当各有弁文。并忘僭留念耳。礼说自为一书。待事力稍敷。追刊似好。未知如何。答道东院任
渴馀甘霈。并惠书苏泻。谨惟酷焰。佥体动止万卫。楼役既至举欐。仰想监董贤劳。慰祝之馀。继庸拱虑。源祚衰力抵不得熇赩。内暍外痱。喘喘欲殊。今日之雨。始有生意抃野之喜。非直沈痾之祛体而已。梁颂初既不敢以匪其人辞。今于指日专价。推诿无路。玆忘僭搆呈。至于楼额。尤不娴于趯啄。而副急挥染。恐不合用奈何。所示三号中。洛一尼洛俱不合于鄙意。盖楼名异于院号。每于虚境而取实义。如庐江之养浩。玉山之无边。道南之静虚是已。故妄以水月命名。秋月照寒水之诗。即千载心法。而先生诗中江心月一舟及只将明月照孤寒之句。与之相符也。未知佥意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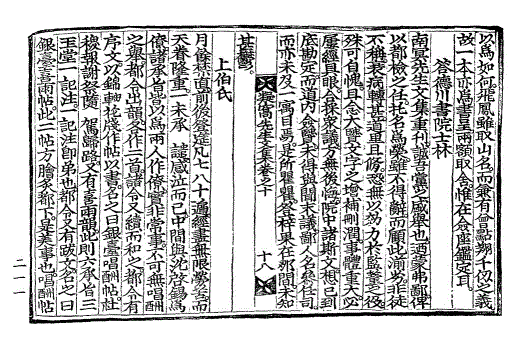 以为如何。飞凤虽取山名。而兼有曾点翔千仞之义。故一本亦为书呈。两额取舍。惟在佥座鉴定耳。
以为如何。飞凤虽取山名。而兼有曾点翔千仞之义。故一本亦为书呈。两额取舍。惟在佥座鉴定耳。答德川书院士林
南冥先生文集重刊。诚吾党之盛举也。乃蒙弗鄙。俾以都检之任。托名为荣。虽不得辞。而顾此湔劣。非徒不称。衰病转甚。道里且脩。恐无以效力于监蕫之役。殊可自愧。且念大贤文字之增补删润。事体重大。必屡经具眼。合采众议。方无后悔。院中诸斯文。想已到底勘定。而道内佥贤。未得与闻末议。鄙人名参任司。而亦未及一寓目焉。是所瞿瞿。登梓果在那间。未知甚郁。
上伯氏
月馀禁直。前后登筵凡七八十遍。经尽无限劳苦。而天眷隆重。一未承 谴。感泣而已。中间与沈启锡为僚。诸承旨皆以为两人作僚。实非常事。不可无唱酬之举。都令出韵。各作二首。诸令又续而和之。都令有序文。以锦轴花笺作帖以书。名之曰银台唱酬帖。社稷报谢祭随 驾归路。又有喜雨韵。此则六承旨三玉堂一记注。一记注即弟也。都令又有跋文。名之曰银台喜雨帖。此二帖方脍炙都下。是美事也。唱酬帖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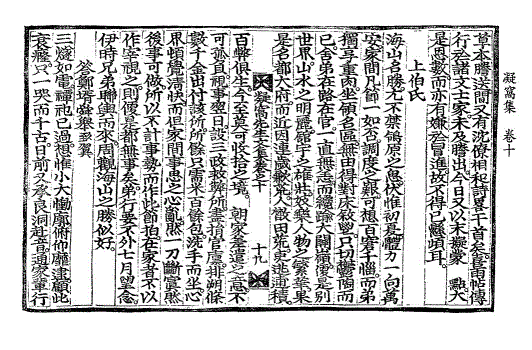 草本誊送。间又有沈僚相和诗略干首矣。喜雨帖传行于诸文士家。未及誊出。今日又以末拟蒙 点。大是恩数。而亦有嫌于冒进。故不得已悬颐耳。
草本誊送。间又有沈僚相和诗略干首矣。喜雨帖传行于诸文士家。未及誊出。今日又以末拟蒙 点。大是恩数。而亦有嫌于冒进。故不得已悬颐耳。上伯氏
海山名胜。尤不禁鸰原之思。伏惟初夏。体力一向万安。家间凡节一如否。调度之艰。可想百窘千恼。而弟独享重肉。坐领名区。无由得对床叙鬯。只切郁陶而已。舍弟在路在官。一直无恙。而才踰大关岭。便是别世界。山水之明丽。馆宇之雄壮。妓乐人物之繁华。果是名都大府。而近因连岁歉荒。人散田荒。吏逃逋积。百弊俱生。今至莫可收拾之境。 朝家差遣之意。不可孤负。视事翌日。设三政救弊所。尽捐官廪。排朔条数千金出付该所。所馀只需米百馀包。洗手而坐。心界顿觉清快。而但家间事思之心乱。然一刀断寘然后事可做。所以不计事势而作此节拍。在家者不以作宰视之。则便是都无事矣。弟行要不外七月望念。伊时兄弟联舆而来。周观海山之胜似好。
答郑婿舜举(致翼)
三燧如电。禫祀已过。想惟小大恸廓。俯仰靡逮。顾此衰癃。只一哭而千古。日前又承良洞赴音。通家辈行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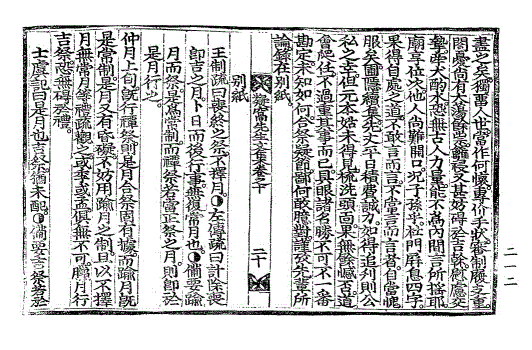 尽之矣。独留人世。当作何怀。专价手状。审制履支重。閤忧尚有大荡馀祟。篱祲又甚妨碍于吉干。慰虑交挚。牵犬酌水。恐无古人力量。能不为内间言所摇耶。庙享位次。他人尚难开口。况子孙乎。杜门屏息四字。果得自处之道。不敢言而言。不当言而言者。自当愧服矣。圃隐续集。先丈平日积费诚力。如得追刊则公私之幸。但元本姑未得见。梳洗头面。果无馀憾否。道会爬任。不过重其事而已。具眼诸名胜不可不一番勘定。未知如何。合祭疑节。鄙何敢臆对。谨考先辈所论。录在别纸。
尽之矣。独留人世。当作何怀。专价手状。审制履支重。閤忧尚有大荡馀祟。篱祲又甚妨碍于吉干。慰虑交挚。牵犬酌水。恐无古人力量。能不为内间言所摇耶。庙享位次。他人尚难开口。况子孙乎。杜门屏息四字。果得自处之道。不敢言而言。不当言而言者。自当愧服矣。圃隐续集。先丈平日积费诚力。如得追刊则公私之幸。但元本姑未得见。梳洗头面。果无馀憾否。道会爬任。不过重其事而已。具眼诸名胜不可不一番勘定。未知如何。合祭疑节。鄙何敢臆对。谨考先辈所论。录在别纸。别纸
王制疏曰丧终之祭。不择月。○左传疏曰计除丧即吉之月。卜日而后行事。无复常月也。○备要踰月而祭。是为常制。而禫祭若当正祭之月。则即于是月行之。
仲月上旬。既行禫祭。则是月合祭固有据。而踰月既是常制。是月又有昏碍。不妨用踰月之制。且以不择月无常月等礼疏观之。或季或孟。俱无不可。腊月行吉祭。恐无碍于礼。
士虞记曰是月也吉祭。犹未配。○备要吉祭若于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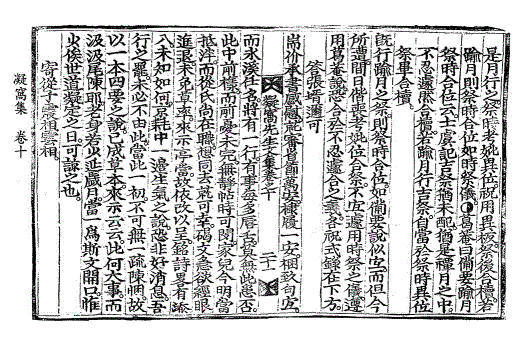 是月行之。祭时考妣异位。祝用异板。祭后合椟。若踰月则祭时合位如时祭仪。○葛庵曰备要踰月祭时合位云。士虞记吉祭犹未配。犹是禫月之中。不忍遽然合椟。若踰月行吉祭。自当于祭时异位。祭毕合椟。
是月行之。祭时考妣异位。祝用异板。祭后合椟。若踰月则祭时合位如时祭仪。○葛庵曰备要踰月祭时合位云。士虞记吉祭犹未配。犹是禫月之中。不忍遽然合椟。若踰月行吉祭。自当于祭时异位。祭毕合椟。既行踰月之祭。则祭时合位。如备要说似宜。而但今所遭。间日偕丧考妣位合祭。不宜遽用时祭之仪。遵用葛庵说。恐合于不忍遽合之义。各祝式录在下方。
答张婿迩可
耑价承书感慰。就审省节万安。棣履一安。梱致匀宜。而冰溪任名。将有一行。有事每多唇舌。莫无此患否。此中前样。而前忧未完。无静帖时可闵。家儿今明当抵泮。而从氏尚在职。想同去就可幸。碣文急欲经眼进退。未免草率。来示亭当。故依改以呈。铭诗略有添入。未知如何。京耗中一边生气之说。恐非好消息。吾行之罢。未必不由此。当此一初。不可无一疏陈悃。故以一本四要之说。已成草本。来示云云。此何大事。而汲汲尾陈耶。老身若少延岁月。当一为斯文开口。惟少俟世道凝定之日。可谅之也。
寄从子震相,云相。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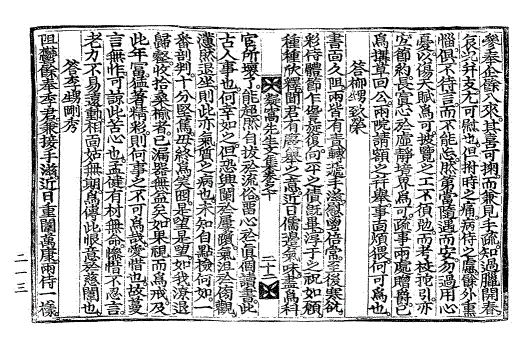 参奉企馀入来。其喜可掬。而兼见手疏。知过腊开春。哀况并支。尤可慰也。但拊时之痛。病侍之虑。馀外熏恼。俱不待言。而不能忘。然第当随遇而安。勿过用心忧。以伤天赋为可。披览之工不须勉。而考校拖引。亦宜节约。长寘心于虚静境界为可。疏事两处赠爵。已为搆草回公。两院请额之并举。事面烦猥。何可为也。
参奉企馀入来。其喜可掬。而兼见手疏。知过腊开春。哀况并支。尤可慰也。但拊时之痛。病侍之虑。馀外熏恼。俱不待言。而不能忘。然第当随遇而安。勿过用心忧。以伤天赋为可。披览之工不须勉。而考校拖引。亦宜节约。长寘心于虚静境界为可。疏事两处赠爵。已为搆草回公。两院请额之并举。事面烦猥。何可为也。答柳甥致荣
书面久阻。两皆有责。转递手滋。慰鬯倍常。至后寒㞃。彩侍体节乍愆旋复。向平之债既毕。淳于之祝如愿。种种欣释。闻君有废举之意。近日儒边气味。尽为科宦所坏了。能超然自拔于流俗。留心于真个读书。此古人事也。何幸如之。但恐兴阑于屡踬。气沮于傍观。懑然退坐。则此亦气质之病也。未知自点检何如。一番剖判。十分坚笃。毋终为笑囮。是望是望。如我潦退归壑。收拾桑榆者。已漏器无益矣。如果视而为戒。及此年富。猛著精彩。则何事之不可为哉。爱惜也。故蔓言无怍。可谅此苦心也。孟健有材无命。惨惜不忍言。老力不易远动。相面姑无期。为传此恨意于慈闱也。
答李甥刚秀
阻郁馀。奉季君。兼接手滋。近日重闱万康。两侍一样。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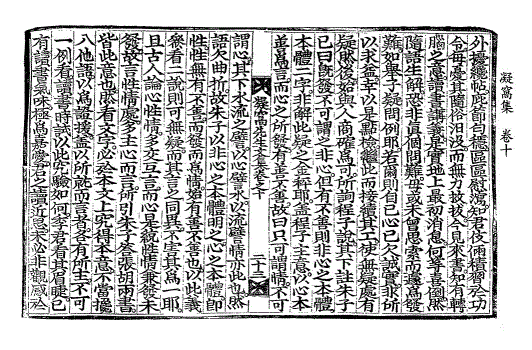 外扰才帖。庇节匀稳。区区慰泻。知君伎俩积习于功令。每忧其随俗汩没。而无力救拔。今见来书。知有转脑之意。读书讲义。是实地上最初消息。何等喜倒。然随语生解。恐非真个问难。毋或未曾思索而遽为发难。如举子疑问例耶。若尔则自己心已欠诚实。非所以求益。幸以是点检。继此而接续其工。使无疑处有疑然后。始与人商确为可。所询程子说。其下注朱子已曰既发不可谓之非心。但有不善则非心之本体。本体二字。非解此疑之金秤耶。盖程子主意。以心本善为言。而心之所发。有善不善。故曰只可谓情。不可谓心。其下水流之譬。以心譬水。以流譬情亦此也。然语欠曲折。故朱子以非心之本体明之。心之本体。即性。性无有不善。而发而为情。始有善不善也。以此义参看二说则可无疑。而其言之同异。不害其为一耶。且古人论心性情。多交互言。而心是统性情兼发未发。故言性情处。多主心而言。所引朱子答张胡两书。皆此意也。然看文字。必于本文上究得本意。不当搀入他语。以为證援。盖以所就而言者。各有所主。不可一例看。读书时试以此究验如何。季君看其眉睫。已有读书气味。极为嘉爱。君之读近思。未必非观感于
外扰才帖。庇节匀稳。区区慰泻。知君伎俩积习于功令。每忧其随俗汩没。而无力救拔。今见来书。知有转脑之意。读书讲义。是实地上最初消息。何等喜倒。然随语生解。恐非真个问难。毋或未曾思索而遽为发难。如举子疑问例耶。若尔则自己心已欠诚实。非所以求益。幸以是点检。继此而接续其工。使无疑处有疑然后。始与人商确为可。所询程子说。其下注朱子已曰既发不可谓之非心。但有不善则非心之本体。本体二字。非解此疑之金秤耶。盖程子主意。以心本善为言。而心之所发。有善不善。故曰只可谓情。不可谓心。其下水流之譬。以心譬水。以流譬情亦此也。然语欠曲折。故朱子以非心之本体明之。心之本体。即性。性无有不善。而发而为情。始有善不善也。以此义参看二说则可无疑。而其言之同异。不害其为一耶。且古人论心性情。多交互言。而心是统性情兼发未发。故言性情处。多主心而言。所引朱子答张胡两书。皆此意也。然看文字。必于本文上究得本意。不当搀入他语。以为證援。盖以所就而言者。各有所主。不可一例看。读书时试以此究验如何。季君看其眉睫。已有读书气味。极为嘉爱。君之读近思。未必非观感于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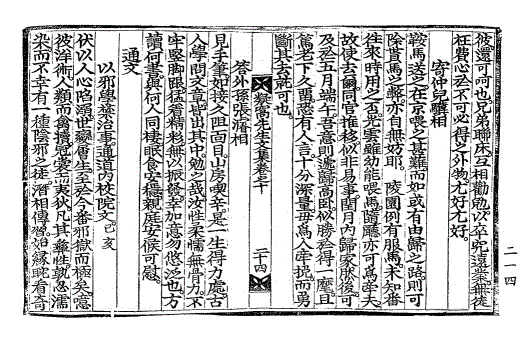 彼。还可呵也。兄弟联床。互相劝勉。以卒究远业。无徒枉费心于不可必得之外物。尤好尤好。
彼。还可呵也。兄弟联床。互相劝勉。以卒究远业。无徒枉费心于不可必得之外物。尤好尤好。寄仲儿骥相
鞍马送之。在京喂之甚难。而如或有由归之路。则可除贳马之弊。亦自无妨耶。 陵园例有服马。未知番往来时用之否。光云虽幼能喂马。随厅亦可为牵夫。故使去尔。同官推移。似非易事。闰月内归家然后。可及于五月端午。吾意则递归高卧。似胜于得一麾。且笃老下久留。恐有人言。十分深量。毋为人牵挽。而勇断其去就可也。
答外孙张浚相
见手笔。如接久阻面目。山房吃辛。是一生得力处。古人学问文章。皆出其中。勉之哉。汝性柔懦无骨力。不牢竖脚跟。猛着精彩。无以振发。幸加意勿悠泛也。方读何书。与何人同栖。眠食安稳。亲庭安候可慰。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通文
以邪学禁治事。通道内校院文。(己亥)
伏以人心陷溺。世变层生。至于今番邪狱而极矣。噫彼洋术。人类而禽犊。冠裳而夷狄。凡其彝性。孰忍濡染。而不幸有一种阴邪之徒。潜相传习。始缘耽看奇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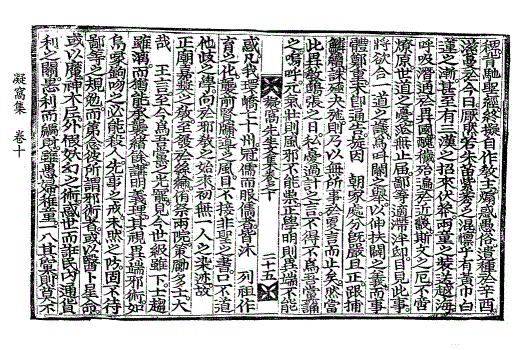 稗。背驰圣经。终拟自作教主。煽惑愚俗。遗种于辛酉。滋蔓于今日。厌然若朱苗紫莠之混。懔乎有黄巾白莲之渐。甚至有三汉之招来伏莽。两童之装送越海。呼吸潜通于异国。丑秽殆遍于近畿。斯文之厄。不啻燎原。世道之忧。茫无止届。鄙等适滞泮邸。目见此事。将欲合一道之议。为叫阍之举。以伸扶辟之义。而事体郑重。未即通告。旋因 朝家处分既严且正。跟捕鳞续。诛殛夬施。则乃以无所事于更言而止矣。然当此异教鸱张之日。私忧过计之言。不得不为吾党诵之。呜呼。元气壮则风邪不能祟。正学明则异端不能惑。凡我环峤七十州。冠儒而服儒者。皆沐 列祖作育之化。袭前贤牖导之风。目不接非圣之书。口不道他岐之学。向于邪教之始来。初无一人之染迹。故 正庙嘉奖之教。至发于丝纶。侑祭两院。策励多士。大哉 王言。至今为吾党之光宠。见今世级虽下。士趋虽漓。而犹能承袭绪馀。讲明义理。其视异端邪术。如乌喙钩吻之必能杀人。先事之戒。未然之防。固不待鄙等之规勉。而第念彼所谓邪术者。或以医卜星命。或以魔神木尼。外假妖幻之术。惑世而䛘(一作诳)民。内通货利之关。思利而骗财。虽愚妇稚童。一入其窠。则莫不
稗。背驰圣经。终拟自作教主。煽惑愚俗。遗种于辛酉。滋蔓于今日。厌然若朱苗紫莠之混。懔乎有黄巾白莲之渐。甚至有三汉之招来伏莽。两童之装送越海。呼吸潜通于异国。丑秽殆遍于近畿。斯文之厄。不啻燎原。世道之忧。茫无止届。鄙等适滞泮邸。目见此事。将欲合一道之议。为叫阍之举。以伸扶辟之义。而事体郑重。未即通告。旋因 朝家处分既严且正。跟捕鳞续。诛殛夬施。则乃以无所事于更言而止矣。然当此异教鸱张之日。私忧过计之言。不得不为吾党诵之。呜呼。元气壮则风邪不能祟。正学明则异端不能惑。凡我环峤七十州。冠儒而服儒者。皆沐 列祖作育之化。袭前贤牖导之风。目不接非圣之书。口不道他岐之学。向于邪教之始来。初无一人之染迹。故 正庙嘉奖之教。至发于丝纶。侑祭两院。策励多士。大哉 王言。至今为吾党之光宠。见今世级虽下。士趋虽漓。而犹能承袭绪馀。讲明义理。其视异端邪术。如乌喙钩吻之必能杀人。先事之戒。未然之防。固不待鄙等之规勉。而第念彼所谓邪术者。或以医卜星命。或以魔神木尼。外假妖幻之术。惑世而䛘(一作诳)民。内通货利之关。思利而骗财。虽愚妇稚童。一入其窠。则莫不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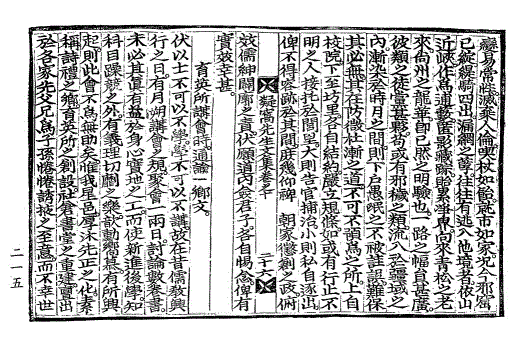 变易常性。灭弃人伦。吃杖如饴。就市如家。况今邪窟已绽。缇骑四出。漏网之孽。往往有逃入他境者。依山近峡。作为逋薮。匿影藏踪。贻累净界。向来青松之老来。尚州之龙华。即已然之明验也。一路之幅员甚广。彼类之徒党甚夥。苟或有邪秽之类。流入于疆域之内。渐染于时月之间。则下户愚氓之不被诖误。难保其必无。其在防微杜渐之道。不可不预为之所。上自校院。下至坊里。各自结约。严立规条。如或有行止不明之人接托于闾里。大则告官捕治。小则私自逐出。俾不得容迹于其间。庶几仰裨 朝家惩创之政。俯效儒绅辟廓之责。伏愿道内佥君子。各自惕念。俾有实效幸甚。
变易常性。灭弃人伦。吃杖如饴。就市如家。况今邪窟已绽。缇骑四出。漏网之孽。往往有逃入他境者。依山近峡。作为逋薮。匿影藏踪。贻累净界。向来青松之老来。尚州之龙华。即已然之明验也。一路之幅员甚广。彼类之徒党甚夥。苟或有邪秽之类。流入于疆域之内。渐染于时月之间。则下户愚氓之不被诖误。难保其必无。其在防微杜渐之道。不可不预为之所。上自校院。下至坊里。各自结约。严立规条。如或有行止不明之人接托于闾里。大则告官捕治。小则私自逐出。俾不得容迹于其间。庶几仰裨 朝家惩创之政。俯效儒绅辟廓之责。伏愿道内佥君子。各自惕念。俾有实效幸甚。育英所讲会时。通谕一乡文。
伏以士不可以不学。学不可以不讲。故在昔儒教兴行之日。有月朔讲会之规。聚会一两日。讨论数卷书。未必其真有益于身心实地之工。而使新进后学。知科目躁竞之外。有义理切劘之乐。歆动向慕。有所兴起。则此会不为无助矣。惟我星邑。厚沐先正之化。素称诗礼之乡。育英所之创设。社仓书堂之重建。亶出于各家先父兄为子孙惓惓诱掖之至意。而不幸世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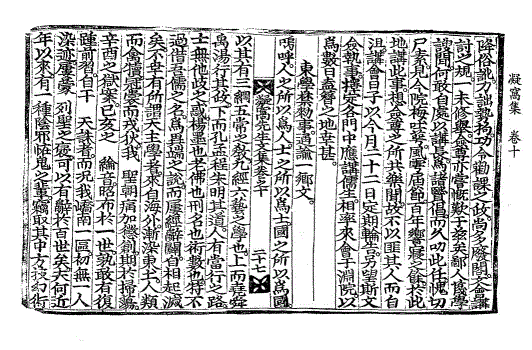 降俗讹。力诎势拘。功令劝课之政。尚多废阁。文会讲讨之规。一未修举。佥尊亦尝慨叹于玆矣。鄙人蔑学謏闻。何敢自处以讲长。为诸贤倡。而久叨此任。愧切尸素。见今院梅吐萼。风雩届节。百年响寝之馀。于此地讲此事。想佥尊之所共乐闻。故不以匪其人而自沮。讲会日子以今月二十二日定期轮告。另望斯文佥执事。择定各门中应讲儒生。相率来会于渊院。以为数日盍簪之地幸甚。
降俗讹。力诎势拘。功令劝课之政。尚多废阁。文会讲讨之规。一未修举。佥尊亦尝慨叹于玆矣。鄙人蔑学謏闻。何敢自处以讲长。为诸贤倡。而久叨此任。愧切尸素。见今院梅吐萼。风雩届节。百年响寝之馀。于此地讲此事。想佥尊之所共乐闻。故不以匪其人而自沮。讲会日子以今月二十二日定期轮告。另望斯文佥执事。择定各门中应讲儒生。相率来会于渊院。以为数日盍簪之地幸甚。东学禁敕事。通谕一乡文。
呜呼。人之所以为人。士之所以为士。国之所以为国。以其有三纲五常之教。九经六艺之学也。上而尧舜禹汤行其政。下而孔孟程朱明其道。人有当行之路。士无他歧之惑。杨墨也老佛也刑名也术数也。特不过借吾儒之名。为异端之说。而屡经辞辟。自相起灭矣。不幸有所谓天主学者。来自海外。渐染东土。人类而禽犊。冠裳而戎狄。我 圣朝痛加惩创。期于扫荡。辛酉之狱案。己亥之 纶音。昭布于一世。孰敢有复踵前习。自干 天诛者。而况我峤南一区。初无一人染迹。屡蒙 列圣之褒。可以有辞于百世矣。夫何近年以来。有一种阴邪怪鬼之辈。窃取其中方技幻术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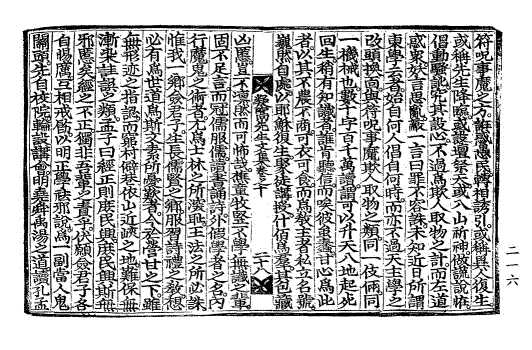 符咒事魔之方。诳惑愚民。转相诱引。或称异人复生。或称先生降临。或设坛祭天。或入山祈神。做谎说怪。倡动骚讹。究其设心。不过为欺人取物之计。而左道惑众。妖言思乱。蔽一言曰罪不容诛。未知近日所谓东学云者。始自何人倡自何时。而亦不过天主学之改头换面。与符咒事魔欺人取物之类。同一伎俩。同一机械也。数十字百千万读。谓可以升天入地起死回生。稍有知识者。谁肯听信。而唉彼蚩蠢。甘心为此者。以其不农不商。可衣可食。而为教主者私立名号。巍然自处。以耶稣复生。聚徒讲授。什佰为群。其包藏凶慝。岂不凛然而可怖哉。樵童牧竖不学无识之辈。固不足言。而冠儒服儒。读书诵诗。外假学者之名。内行魔鬼之术者。尤为士林之所深耻。王法之所必诛。惟我一乡佥君子。生长儒贤之乡。服习诗礼之教。想必有为世道为斯文素所忧叹者。今于营甘之下。虽无形迹之指认。而穷村僻巷依山近峡之地。难保无渐染诖误之类。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经之不正。独非吾辈之责乎。伏愿佥君子各自惕厉。互相戒饬。以明正学祛邪说。为一副当人鬼关头。先自校院。轮设讲会。明尧舜禹汤之道。读孔孟
符咒事魔之方。诳惑愚民。转相诱引。或称异人复生。或称先生降临。或设坛祭天。或入山祈神。做谎说怪。倡动骚讹。究其设心。不过为欺人取物之计。而左道惑众。妖言思乱。蔽一言曰罪不容诛。未知近日所谓东学云者。始自何人倡自何时。而亦不过天主学之改头换面。与符咒事魔欺人取物之类。同一伎俩。同一机械也。数十字百千万读。谓可以升天入地起死回生。稍有知识者。谁肯听信。而唉彼蚩蠢。甘心为此者。以其不农不商。可衣可食。而为教主者私立名号。巍然自处。以耶稣复生。聚徒讲授。什佰为群。其包藏凶慝。岂不凛然而可怖哉。樵童牧竖不学无识之辈。固不足言。而冠儒服儒。读书诵诗。外假学者之名。内行魔鬼之术者。尤为士林之所深耻。王法之所必诛。惟我一乡佥君子。生长儒贤之乡。服习诗礼之教。想必有为世道为斯文素所忧叹者。今于营甘之下。虽无形迹之指认。而穷村僻巷依山近峡之地。难保无渐染诖误之类。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经之不正。独非吾辈之责乎。伏愿佥君子各自惕厉。互相戒饬。以明正学祛邪说。为一副当人鬼关头。先自校院。轮设讲会。明尧舜禹汤之道。读孔孟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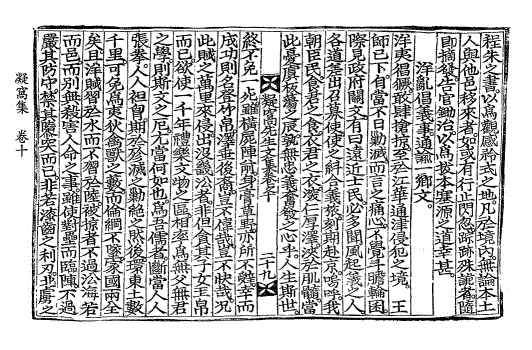 程朱之书。以为观感矜式之地。凡于境内。无论本土人与他邑移来者。如或有行止闪忽。踪迹殊诡者。随即摘发。告官锄治。以为拔本塞源之道幸甚。
程朱之书。以为观感矜式之地。凡于境内。无论本土人与他邑移来者。如或有行止闪忽。踪迹殊诡者。随即摘发。告官锄治。以为拔本塞源之道幸甚。洋乱倡义事。通谕一乡文。
洋夷猖獗。敢肆抢掠。至于江华通津侵犯之境。 王师已下。自当不日剿灭。而言之痛心。不觉斗胆轮囷。际见政府关文。有曰远近士民。必多闻风起义之人。各道差出召募使。使之纠合义旅。刻期赴京。呜呼。我朝臣民。食君之食。衣君之衣。深仁厚泽。浃于肌髓。当此忧虞板荡之辰。孰无忠义奋发之心乎。人生斯世。终不免一死。虽横尸阵前。身膏草野。亦所不辞。幸而成功则名登竹帛。泽垂后裔。岂不伟哉。岂不快哉。况此贼之万里来侵。出没畿沿者。非但贪其子女玉帛而已。欲使一千年礼乐文物之区。相率为无父无君之学。则斯文之厄。尤当何如也。为吾儒者。断当人人张拳。人人袒胸。期于殄灭之剿绝之然后。环东土数千里。可免为夷狄禽兽之薮。而伦纲不坠。家国两全矣。且洋贼习于水而不习于陆。被掠者不过沿海若而邑。而别无杀害人命之事。虽使对垒而临阵。不过严其防守。禁其隳突而已。非若漆齿之利刃。北虏之
凝窝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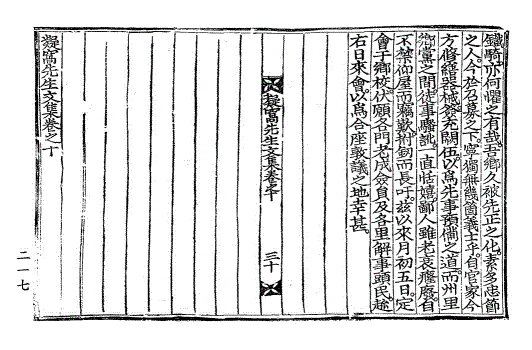 铁骑。亦何惧之有哉。吾乡久被先正之化。素多忠节之人。今于召募之下。宁独无几个义士乎。自官家今方修缮器械。签充阙伍。以为先事预备之道。而州里乡党之间。徒事骚讹。一直恬嬉。鄙人虽老衰癃废。自不禁仰屋而窃叹。拊釰而长吁。玆以来月初五日。定会于乡校。伏愿各门老成佥员及各里解事头民。趁右日来会。以为合座敦议之地幸甚。
铁骑。亦何惧之有哉。吾乡久被先正之化。素多忠节之人。今于召募之下。宁独无几个义士乎。自官家今方修缮器械。签充阙伍。以为先事预备之道。而州里乡党之间。徒事骚讹。一直恬嬉。鄙人虽老衰癃废。自不禁仰屋而窃叹。拊釰而长吁。玆以来月初五日。定会于乡校。伏愿各门老成佥员及各里解事头民。趁右日来会。以为合座敦议之地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