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箴
自省箴
我事是非。我心已烛。我苟是矣。我心快足。我苟非矣。我心歉蹙。上天寔临。莫显于独。无负我心。庶几无怍。
慎独箴
事之隐微。人皆谓独。其机已动。难掩其独。
心之几微。是之谓独。天神所知。盍慎其独。
箴
自省箴
我事是非。我心已烛。我苟是矣。我心快足。我苟非矣。我心歉蹙。上天寔临。莫显于独。无负我心。庶几无怍。
慎独箴
事之隐微。人皆谓独。其机已动。难掩其独。
心之几微。是之谓独。天神所知。盍慎其独。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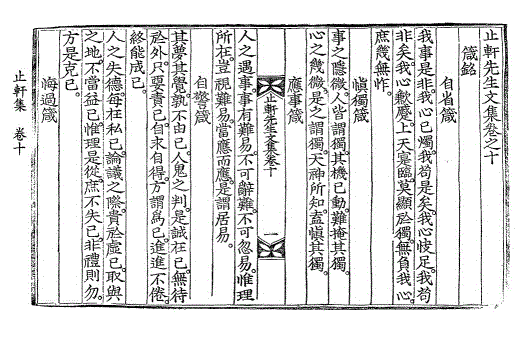 应事箴
应事箴人之遇事。事有难易。不可辞难。不可忽易。惟理所在。岂视难易。当应而应。是谓居易。
自警箴
其梦其觉。孰不由己。人鬼之判。是诚在己。无待于外。只要责己。自求自得。方谓为己。进进不倦。终能成己。
人之失德。每在私己。论议之际。贵于虚己。取与之地。不当益己。惟理是从。庶不失己。非礼则勿。方是克己。
悔过箴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1L 页
 事过难追。是以有悔。所贵乎悔。以其能改。能改之方。阙疑阙殆。慎言慎行。圣训昭在。
事过难追。是以有悔。所贵乎悔。以其能改。能改之方。阙疑阙殆。慎言慎行。圣训昭在。恕箴
所好所恶。亿兆皆同。心之所推。宁使不同。
恕之为义。以其如心。既尽我心。曷违人心。
语默箴
当默而默。当言而言。苟失其宜。均之为愆。
戒名箴
名虽随迹。无与于实。过情之闻。已非其实。务外而得。固无其实。自谓不求。犹未为实。默默自守。方是从实。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铭
潜字铭
窗明帝对。屋漏神临。所以修之潜。毫釐必辨。路脉是寻。是以思之潜。
乌竹杖铭
内白外玄。其象金水。发笋重包。三缄无累。节节盈科。其终如始。
金水之精。其理属静。当动而动。固非耽静。于止而止。亦云主静。
木桥铭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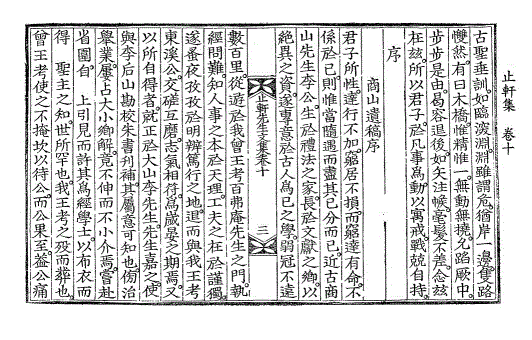 古圣垂训。如临深渊。渊虽谓危。犹岸一边。只路𢥠然。有曰本桥。惟精惟一。无动无挠。允蹈厥中。步步是由。曷容退后。如矢注帿。毫发不差。念玆在玆。所以君子。于凡事为。动以寓戒。战兢自持。
古圣垂训。如临深渊。渊虽谓危。犹岸一边。只路𢥠然。有曰本桥。惟精惟一。无动无挠。允蹈厥中。步步是由。曷容退后。如矢注帿。毫发不差。念玆在玆。所以君子。于凡事为。动以寓戒。战兢自持。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商山遗稿序
君子所性。达行不加。穷居不损。而穷达有命。不系于己。则惟当随遇而尽其己分而已。近古商山先生李公。生于礼法之家。长于文献之乡。以绝异之资。遂专意于古人为己之学。弱冠不远数百里。从游于我曾王考百弗庵先生之门。执经问难。知人事之本于天理。工夫之在于谨独。遂蚤夜孜孜于明辨笃行之地。退而与我王考东溪公。交磋互磨。志气相符。为岁晏之期焉。又以所自得者。就正于大山李先生。先生嘉之。使与李后山勘校朱书刊补。其属意可知也。傍治举业。屡占大小乡解。竟不伸而不小介焉。尝赴省围。自 上引见而许其为经学士。以布衣而得 圣主之知。世所罕也。我王考之殁而葬也。曾王考使之不掩坎以待公。而公果至。盖公痛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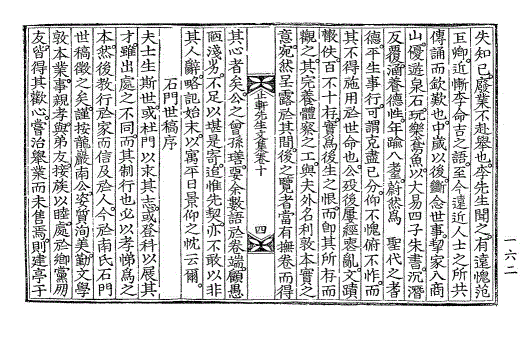 失知己。废业不赴举也。李先生闻之。有远愧范巨卿。近惭李命吉之语。至今远近人士之所共传诵而钦叹也。中岁以后。断念世事。挈家入商山。优游泉石。玩乐鸢鱼。以大易四子朱书。沉潜反覆。涵养德性。年踰八耋。蔚然为 圣代之耆德。平生事行。可谓克尽己分。仰不愧俯不怍。而其不得施用于世命也。公殁后屡经丧乱。文迹散佚。百不十存。实为后生之恨。而即其所存而观之。其完养体察之工。与夫外名利敦本实之意。宛然呈露于其间。后之览者当有抚卷而得其心者矣。公之曾孙𤩕。要余数语于卷端。顾愚陋浅劣。不足以堪是寄。追惟先契。亦不敢以非其人辞。略记始末。以寓平日景仰之忱云尔。
失知己。废业不赴举也。李先生闻之。有远愧范巨卿。近惭李命吉之语。至今远近人士之所共传诵而钦叹也。中岁以后。断念世事。挈家入商山。优游泉石。玩乐鸢鱼。以大易四子朱书。沉潜反覆。涵养德性。年踰八耋。蔚然为 圣代之耆德。平生事行。可谓克尽己分。仰不愧俯不怍。而其不得施用于世命也。公殁后屡经丧乱。文迹散佚。百不十存。实为后生之恨。而即其所存而观之。其完养体察之工。与夫外名利敦本实之意。宛然呈露于其间。后之览者当有抚卷而得其心者矣。公之曾孙𤩕。要余数语于卷端。顾愚陋浅劣。不足以堪是寄。追惟先契。亦不敢以非其人辞。略记始末。以寓平日景仰之忱云尔。石门世稿序
夫士生斯世。或杜门以求其志。或登科以展其才。虽出处之不同。而其制行也必以孝悌为之本。然后教行于家而信及于人。今于南氏石门世稿徵之矣。谨按龙岩南公。姿质洵美。勤文学敦本业。事亲孝。与弟友。接族以睦。处于乡党朋友。皆得其欢心。尝治举业而未售焉。则建亭于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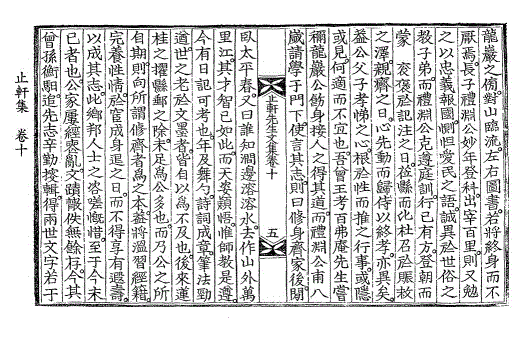 龙岩之傍。对山临流。左右图书。若将终身而不厌焉。长子礼渊公妙年登科。出宰百里。则又勉之以忠义报国。恻怛爱民之语。诚异于世俗之教子弟。而礼渊公克遵庭训。行己有方。登朝而蒙 衮褒于记注之日。莅县而比杜召于赈救之泽。亲癠之日。心先动而归侍以终孝。亦异矣。盖公父子孝悌之心。根于性而推之行事。或隐或见。何适而不宜也。吾曾王考百弗庵先生尝称龙岩公饬身接人之得其道。而礼渊公甫八岁请学于门下。使言其志。则曰修身齐家后。閒卧太平春。又曰谁知涧边溶溶水。去作山外万里江。其才智已如此。而天姿颖悟。惟师教是遵。今有日记可考也。年及舞勺。诗词成章。笔法劲遒。世之老于文墨者。皆自以为不及也。后来莲桂之擢县邮之除。未足为公多也。而乃公之所自期。则向所谓修齐者为之本。盖将温习经籍。完养性情。于宦成身退之日。而不得享有遐寿。以成其志。此乡邦人士之咨嗟慨惜。至于今未已者也。公家屡经丧乱。文迹散佚无馀存。今其曾孙衡驲。追先志辛勤搜辑。得两世文字若干
龙岩之傍。对山临流。左右图书。若将终身而不厌焉。长子礼渊公妙年登科。出宰百里。则又勉之以忠义报国。恻怛爱民之语。诚异于世俗之教子弟。而礼渊公克遵庭训。行己有方。登朝而蒙 衮褒于记注之日。莅县而比杜召于赈救之泽。亲癠之日。心先动而归侍以终孝。亦异矣。盖公父子孝悌之心。根于性而推之行事。或隐或见。何适而不宜也。吾曾王考百弗庵先生尝称龙岩公饬身接人之得其道。而礼渊公甫八岁请学于门下。使言其志。则曰修身齐家后。閒卧太平春。又曰谁知涧边溶溶水。去作山外万里江。其才智已如此。而天姿颖悟。惟师教是遵。今有日记可考也。年及舞勺。诗词成章。笔法劲遒。世之老于文墨者。皆自以为不及也。后来莲桂之擢县邮之除。未足为公多也。而乃公之所自期。则向所谓修齐者为之本。盖将温习经籍。完养性情。于宦成身退之日。而不得享有遐寿。以成其志。此乡邦人士之咨嗟慨惜。至于今未已者也。公家屡经丧乱。文迹散佚无馀存。今其曾孙衡驲。追先志辛勤搜辑。得两世文字若干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3L 页
 篇。名之曰石门世稿。盖龙岩礼渊当日栖息自号之地。皆在石门之内也。即是而览焉。则抱书卧云之趣。为国忠爱之忱。与夫勤文学敦孝友之实迹。犹可以徵其万一矣。衡驲甫要余一言于卷中。余固见识粗浅。不敢为人作文字。特以先分之厚。而其孝思又足以感人。不敢终辞。略记其颠末如右。
篇。名之曰石门世稿。盖龙岩礼渊当日栖息自号之地。皆在石门之内也。即是而览焉。则抱书卧云之趣。为国忠爱之忱。与夫勤文学敦孝友之实迹。犹可以徵其万一矣。衡驲甫要余一言于卷中。余固见识粗浅。不敢为人作文字。特以先分之厚。而其孝思又足以感人。不敢终辞。略记其颠末如右。月厓遗稿序
自古怀德抱才之士。达而用于时。则佐治救俗之方。未尝不在其分内。然穷而处乎野。则其所以为业者。不过文墨书史以自娱。而勉勉于自己分上而已。近古月厓处士。即吾族曾大父也。以仁厚之资。兼通敏之才。事亲孝与弟友。睦于宗族。信于朋友。而济人之急。恤人之困。其素所蓄积也。所在输诚。无不称情。声名洋溢于乡邦。以至道路舆儓之贱。咸啧啧焉。使公得进用而展其所蕴。则仁声之感人。惠泽之及物。为如何哉。尝治公车业。不得售于有司。则四方之志休矣。筑书斋于达理洞先山下。插万卷书其中。左抽右披。昼读夜诵。间又游咏于山颠水厓之间。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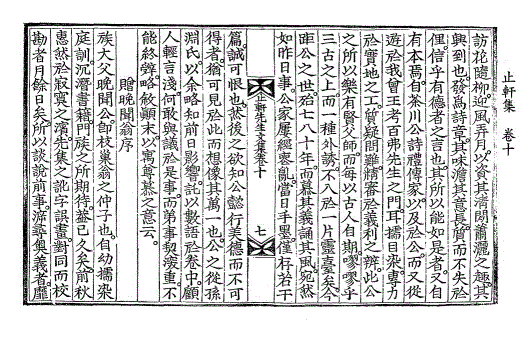 访花随柳。迎风弄月。以资其清閒萧洒之趣。其兴到也。发为诗章。其味澹其意长。质而不失于俚。信乎有德者之言也。其所以能如是者。又自有本焉。自茶川公诗礼传家。以及于公。而又从游于我曾王考百弗先生之门。耳擩目染。专力于实地之工。质疑问难。精审于义利之辨。此公之所以乐有贤父师。而每以古人自期。嘐嘐乎三古之上。而一种外诱。不入于一片灵台矣。今距公之世。殆七八十年。而慕其义诵其风。宛然如昨日事。公家屡经丧乱。当日手墨。仅存若干篇。诚可恨也。然后之欲知公懿行美德而不可得者。犹可见于此而想像其万一也。公之从孙渊氏。以余略知前日影响。托以数语于卷中。顾人轻言浅。何敢与议于是事。而第事契深重。不能终辞。略叙颠末。以寓尊慕之意云。
访花随柳。迎风弄月。以资其清閒萧洒之趣。其兴到也。发为诗章。其味澹其意长。质而不失于俚。信乎有德者之言也。其所以能如是者。又自有本焉。自茶川公诗礼传家。以及于公。而又从游于我曾王考百弗先生之门。耳擩目染。专力于实地之工。质疑问难。精审于义利之辨。此公之所以乐有贤父师。而每以古人自期。嘐嘐乎三古之上。而一种外诱。不入于一片灵台矣。今距公之世。殆七八十年。而慕其义诵其风。宛然如昨日事。公家屡经丧乱。当日手墨。仅存若干篇。诚可恨也。然后之欲知公懿行美德而不可得者。犹可见于此而想像其万一也。公之从孙渊氏。以余略知前日影响。托以数语于卷中。顾人轻言浅。何敢与议于是事。而第事契深重。不能终辞。略叙颠末。以寓尊慕之意云。赠晚闻翁序
族大父晚闻公。即枝巢翁之仲子也。自幼擩染庭训。沉潜书籍。门族之所期待。盖已久矣。前秋惠然于寂寞之滨。先集之讹字误画。对同而校勘者月馀日矣。所以谈说前事。溯寻奥义者。靡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4L 页
 有馀地。又傍及于古人性理文字。与夫作者轨范。以之上下数千载之间。所以鼓发精神。勉进步趋者。殆竭其力之所及矣。当其深夜清晨。从容晤语前日之所经历。后来之所酬接。无不讲磨而商量。于是乎尽其心之所知而无馀蕴矣。顾此驽劣最出人下。未能粗寻家学。自恐前头为凡夫不得。而徒以天亲之懿。先分之笃。获陪先进之侧。款听深到之论。其所然诺相与之义。实有他人所不可得者。公方欿然自视。思所以日新其业。将有以进步竿头。克绍先绪。后生取善之益。又何可量耶。第念青蝇之附骥也。祇托以自致耳。未为少补于逸步。而骥之不挥而去之者。自不害为大度之一事。将命者闻此言。未知以为如何。
有馀地。又傍及于古人性理文字。与夫作者轨范。以之上下数千载之间。所以鼓发精神。勉进步趋者。殆竭其力之所及矣。当其深夜清晨。从容晤语前日之所经历。后来之所酬接。无不讲磨而商量。于是乎尽其心之所知而无馀蕴矣。顾此驽劣最出人下。未能粗寻家学。自恐前头为凡夫不得。而徒以天亲之懿。先分之笃。获陪先进之侧。款听深到之论。其所然诺相与之义。实有他人所不可得者。公方欿然自视。思所以日新其业。将有以进步竿头。克绍先绪。后生取善之益。又何可量耶。第念青蝇之附骥也。祇托以自致耳。未为少补于逸步。而骥之不挥而去之者。自不害为大度之一事。将命者闻此言。未知以为如何。四院讲录序
吾乡素称文献之邦。鸿硕迭作。儒化大明。时则通乡月朔之讲。传为兴励之具。庠塾之间。经诵相传。逮至近世。则遂寝而不行。讲规虽存。而仅为各门之设而已。岁丁卯春。乡儒士慨然欲申明旧制。乃自江北四院。将为施设。而岁荒财匮。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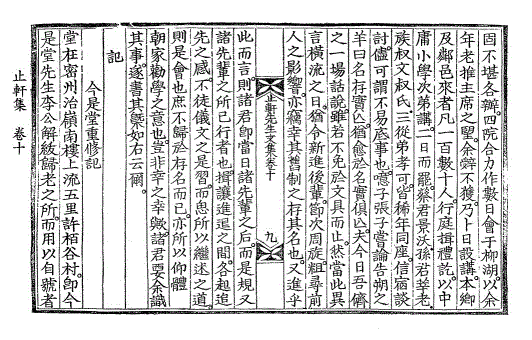 固不堪各办。四院合力作数日会于柳湖。以余年老推主席之望。余辞不获。乃卜日设讲。本乡及邻邑来者凡一百数十人。行庭揖礼讫。以中庸小学次第讲。二日而罢。蔡君景沃,孙君莘老,族叔文叔氏,三从弟孝可。皆稀年同座。信宿谈讨。尽可谓不易底事也。噫子张子尝论告朔之羊曰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夫今日吾侪之一场话说。虽若不免于文具而止。然当此异言横流之日。犹令新进后辈。节次周旋。粗寻前人之影响。亦窃幸其旧制之存其名也。又进乎此而言。则诸君即当日诸先辈之后。而是规又诸先辈之所已行者也。揖让进退之间。各起追先之感。不徒仪文之是习。而思所以继述之道。则是会也庶不归于存名而已。亦所以仰体 朝家劝学之意也。岂非幸之幸欤。诸君要余识其事。遂书其槩如右云尔。
固不堪各办。四院合力作数日会于柳湖。以余年老推主席之望。余辞不获。乃卜日设讲。本乡及邻邑来者凡一百数十人。行庭揖礼讫。以中庸小学次第讲。二日而罢。蔡君景沃,孙君莘老,族叔文叔氏,三从弟孝可。皆稀年同座。信宿谈讨。尽可谓不易底事也。噫子张子尝论告朔之羊曰名存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夫今日吾侪之一场话说。虽若不免于文具而止。然当此异言横流之日。犹令新进后辈。节次周旋。粗寻前人之影响。亦窃幸其旧制之存其名也。又进乎此而言。则诸君即当日诸先辈之后。而是规又诸先辈之所已行者也。揖让进退之间。各起追先之感。不徒仪文之是习。而思所以继述之道。则是会也庶不归于存名而已。亦所以仰体 朝家劝学之意也。岂非幸之幸欤。诸君要余识其事。遂书其槩如右云尔。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记
今是堂重修记
堂在密州治岭南楼上流五里许柏谷村。即今是堂先生李公解绂归老之所。而用以自号者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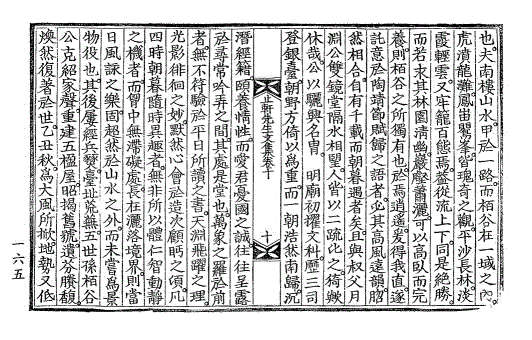 也。夫南楼山水。甲于一路。而柏谷在一域之内。虎濆龙滩。凤岫莺峰。皆瑰奇之观。平沙长林。淡霞轻云。又牢笼百态焉。盖从流上下。同是绝胜。而若求其林园清幽。岩壑萧洒。可以高卧而完养。则柏谷之所独有也。于焉逍遥。爰得我直。遂托意于陶靖节赋归之语者。必其高风远韵。吻然相合。自有千载而朝暮遇者矣。且与叔父月渊公双镜堂隔水相望。人皆以二疏比之。猗欤休哉。公以骊兴名胄。 明庙初擢文科。历三司登银台。朝野方倚以为重。而一朝浩然南归。沉潜经籍。颐养情性。而爱君忧国之诚。往往呈露于寻常吟弄之间。其处是堂也。万象之罗于前者。无不符验于平日所读之书。天渊飞跃之理。光影徘徊之妙。默然心会于造次顾眄之顷。凡四时朝暮随时异趣者。无非所以体仁智动静之机者。而胸中无滞碍处。长在洒落境界。则当日风咏之乐。固超然于山水之外。而未尝为景物役也。其后屡经兵燹。台址荒芜。五世孙柏谷公克绍家声。重建五楹屋。昭揭旧号。遗芬剩馥。焕然复著于世。乙丑秋。为大风所掀。地势又低
也。夫南楼山水。甲于一路。而柏谷在一域之内。虎濆龙滩。凤岫莺峰。皆瑰奇之观。平沙长林。淡霞轻云。又牢笼百态焉。盖从流上下。同是绝胜。而若求其林园清幽。岩壑萧洒。可以高卧而完养。则柏谷之所独有也。于焉逍遥。爰得我直。遂托意于陶靖节赋归之语者。必其高风远韵。吻然相合。自有千载而朝暮遇者矣。且与叔父月渊公双镜堂隔水相望。人皆以二疏比之。猗欤休哉。公以骊兴名胄。 明庙初擢文科。历三司登银台。朝野方倚以为重。而一朝浩然南归。沉潜经籍。颐养情性。而爱君忧国之诚。往往呈露于寻常吟弄之间。其处是堂也。万象之罗于前者。无不符验于平日所读之书。天渊飞跃之理。光影徘徊之妙。默然心会于造次顾眄之顷。凡四时朝暮随时异趣者。无非所以体仁智动静之机者。而胸中无滞碍处。长在洒落境界。则当日风咏之乐。固超然于山水之外。而未尝为景物役也。其后屡经兵燹。台址荒芜。五世孙柏谷公克绍家声。重建五楹屋。昭揭旧号。遗芬剩馥。焕然复著于世。乙丑秋。为大风所掀。地势又低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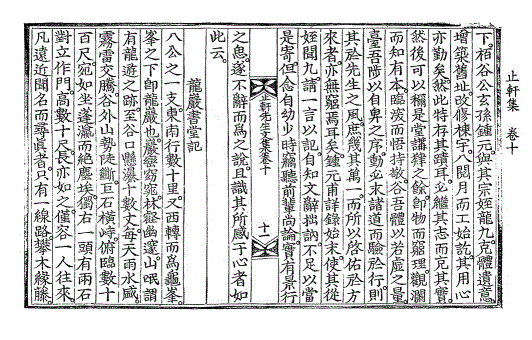 下。柏谷公玄孙钟元。与其宗侄龙九。克体遗意。增筑旧址。改修栋宇。八阅月而工始讫。其用心亦勤矣。然此特存其迹耳。必继其志而充其实。然后可以称是堂讲肄之馀。即物而穷理。观澜而知有本。临深而悟持敬。谷吾体以若虚之量。台吾陟以自卑之序。动必求诸道而验于行。则其于先生之风。庶几其万一。而所以启佑于方来者。亦无穷焉耳矣。钟元甫详录始末。使其从侄闻九。请一言以记。自知文辞拙讷。不足以当是寄。但念自幼少时窃听前辈尚论。实有景行之思。遂不辞而为之说。且识其所感于心者如此云。
下。柏谷公玄孙钟元。与其宗侄龙九。克体遗意。增筑旧址。改修栋宇。八阅月而工始讫。其用心亦勤矣。然此特存其迹耳。必继其志而充其实。然后可以称是堂讲肄之馀。即物而穷理。观澜而知有本。临深而悟持敬。谷吾体以若虚之量。台吾陟以自卑之序。动必求诸道而验于行。则其于先生之风。庶几其万一。而所以启佑于方来者。亦无穷焉耳矣。钟元甫详录始末。使其从侄闻九。请一言以记。自知文辞拙讷。不足以当是寄。但念自幼少时窃听前辈尚论。实有景行之思。遂不辞而为之说。且识其所感于心者如此云。龙岩书堂记
八公之一支。东南行数十里。又西转而为龟峰。峰之下即龙岩也。岩峦窈窕。林壑幽邃。山氓谓有龙游之迹。至谷口悬瀑十数丈。每天雨水盛。雾雷交腾。谷外山势陡断。巨石横峙。俯临数十百尺。宛如坐蓬瀛而绝尘埃。独右一头有两石对立作门。高数十尺。长亦如之。仅容一人往来。凡远近闻名而寻真者。只有一线路。攀木缘藤。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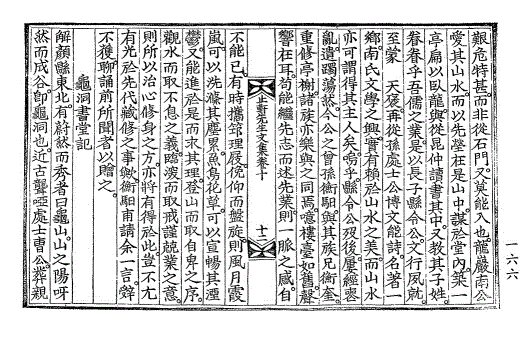 艰危特甚。而非从石门。又莫能入也。龙岩南公爱其山水。而以先茔在是山中。谋于堂内。筑一亭扁以卧龙。与从昆仲读书其中。又教其子姓。眷眷乎吾儒之业。是以长子县令公。文行夙就。至蒙 天褒。再从孙处士公博文能诗。名著一乡。南氏文学之兴。实有赖于山水之美。而山水亦可谓得其主人矣。呜乎。县令公殁后。屡经丧乱。遗躅荡然。今公之曾孙衡驲。与其族兄衡奎。重修亭榭。诸族亦乐与之同焉。噫楼台如旧。声响在耳。苟能继先志而述先业。则一脉之感。自不能已。有时携筇理屐。俛仰而盘旋。则风月霞岚。可以洗涤其尘累。鱼鸟花草。可以宣畅其湮郁。又能进于是而求其理。登山而取自卑之序。观水而取不息之义。临深而取戒谨兢业之意。则所以治心修身之方。亦将有得于此。岂不尤有光于先代藏修之事欤。衡驲甫请余一言。辞不获。聊诵前所闻者以赠之。
艰危特甚。而非从石门。又莫能入也。龙岩南公爱其山水。而以先茔在是山中。谋于堂内。筑一亭扁以卧龙。与从昆仲读书其中。又教其子姓。眷眷乎吾儒之业。是以长子县令公。文行夙就。至蒙 天褒。再从孙处士公博文能诗。名著一乡。南氏文学之兴。实有赖于山水之美。而山水亦可谓得其主人矣。呜乎。县令公殁后。屡经丧乱。遗躅荡然。今公之曾孙衡驲。与其族兄衡奎。重修亭榭。诸族亦乐与之同焉。噫楼台如旧。声响在耳。苟能继先志而述先业。则一脉之感。自不能已。有时携筇理屐。俛仰而盘旋。则风月霞岚。可以洗涤其尘累。鱼鸟花草。可以宣畅其湮郁。又能进于是而求其理。登山而取自卑之序。观水而取不息之义。临深而取戒谨兢业之意。则所以治心修身之方。亦将有得于此。岂不尤有光于先代藏修之事欤。衡驲甫请余一言。辞不获。聊诵前所闻者以赠之。龟洞书堂记
解颜县东北。有蔚然而秀者曰龟山。山之阳呀然而成谷。即龟洞也。近古聋哑处士曹公。葬亲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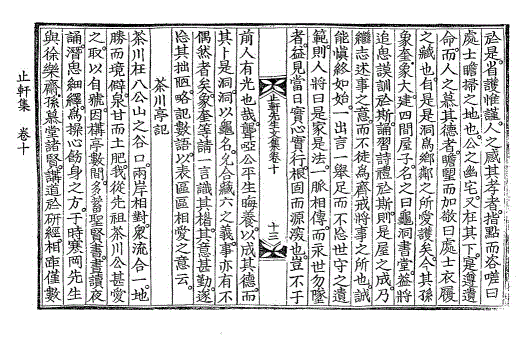 于是。省护惟谨。人之感其孝者。指点而咨嗟曰处士瞻扫之地也。公之幽宅。又在其下。寔遵遗命。而人之慕其德者。瞻望而加敬曰处士衣履之藏也。自是是洞为乡邻之所爱护矣。今其孙象奎,象大。建四间屋子。名之曰龟洞书堂。盖将追思谟训于斯。诵习诗礼于斯。则是屋之成。乃继志述事之意。而不徒为齐戒将事之所也。诚能慎终如始。一出言一举足而不忘世守之遗范。则人将曰是家是法。一脉相传。而永世勿坠者。益见当日实心实行。根固而源深也。岂不于前人有光也哉。聋哑公平生晦养。以成其德。而其卜是洞。洞以龟名。允合藏六之义。事亦有不偶然者矣。象奎等请一言识其楣。其意甚勤。遂忘其拙陋。略记数语。以表区区相爱之意云。
于是。省护惟谨。人之感其孝者。指点而咨嗟曰处士瞻扫之地也。公之幽宅。又在其下。寔遵遗命。而人之慕其德者。瞻望而加敬曰处士衣履之藏也。自是是洞为乡邻之所爱护矣。今其孙象奎,象大。建四间屋子。名之曰龟洞书堂。盖将追思谟训于斯。诵习诗礼于斯。则是屋之成。乃继志述事之意。而不徒为齐戒将事之所也。诚能慎终如始。一出言一举足而不忘世守之遗范。则人将曰是家是法。一脉相传。而永世勿坠者。益见当日实心实行。根固而源深也。岂不于前人有光也哉。聋哑公平生晦养。以成其德。而其卜是洞。洞以龟名。允合藏六之义。事亦有不偶然者矣。象奎等请一言识其楣。其意甚勤。遂忘其拙陋。略记数语。以表区区相爱之意云。茶川亭记
茶川在八公山之谷口。两岸相对。众流合一。地胜而境僻。泉甘而土肥。我从先祖茶川公甚爱之。取以自号。因构亭数间。多蓄圣贤书。昼读夜诵。潜思细绎。为操心饬身之方。于时寒冈先生与徐乐斋,孙慕堂诸贤。讲道于研经。相距仅数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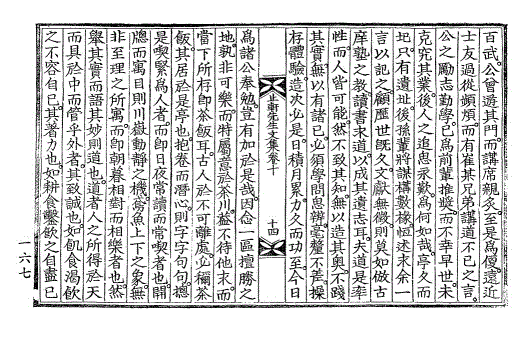 百武。公曾游其门。而讲席亲炙。至是为便。远近士友过从频烦。而有崔某兄弟讲道不已之言。公之励志勤学。已为前辈推奖。而不幸早世。未克究其业。后人之追思永叹。为何如哉。亭久而圮。只有遗址。后孙辈将谋构数椽。恒述求余一言以记之。顾历世既久。文献无徵。则莫如仿古庠塾之教。读书求道。以成其遗志耳。夫道是率性。而人皆可能。然不致其知。无以造其奥。不践其实。无以有诸己。必须学问思辨。毫釐不差。操存体验。造次必是。日积月累。力久而功至。今日为诸公奉勉。岂有加于是哉。因念一区擅胜之地。孰非可乐。而特属意于茶川。盖不待他求。而当下所存即茶饭耳。古人于不可离处。必称茶饭。其居于是亭也。抱卷而潜心。则字字句句。总是吃紧为人者。而即日夜常读而常吃者也。开窗而寓目则川岳动静之机。鸢鱼上下之象。无非至理之所寓。而即朝暮相对而相乐者也。然举其实而语其妙则道也。道者人之所得于天而具于中而管乎外者。其致诚也。如饥食渴饮之不容自已。其著力也。如耕食凿饮之自尽己
百武。公曾游其门。而讲席亲炙。至是为便。远近士友过从频烦。而有崔某兄弟讲道不已之言。公之励志勤学。已为前辈推奖。而不幸早世。未克究其业。后人之追思永叹。为何如哉。亭久而圮。只有遗址。后孙辈将谋构数椽。恒述求余一言以记之。顾历世既久。文献无徵。则莫如仿古庠塾之教。读书求道。以成其遗志耳。夫道是率性。而人皆可能。然不致其知。无以造其奥。不践其实。无以有诸己。必须学问思辨。毫釐不差。操存体验。造次必是。日积月累。力久而功至。今日为诸公奉勉。岂有加于是哉。因念一区擅胜之地。孰非可乐。而特属意于茶川。盖不待他求。而当下所存即茶饭耳。古人于不可离处。必称茶饭。其居于是亭也。抱卷而潜心。则字字句句。总是吃紧为人者。而即日夜常读而常吃者也。开窗而寓目则川岳动静之机。鸢鱼上下之象。无非至理之所寓。而即朝暮相对而相乐者也。然举其实而语其妙则道也。道者人之所得于天而具于中而管乎外者。其致诚也。如饥食渴饮之不容自已。其著力也。如耕食凿饮之自尽己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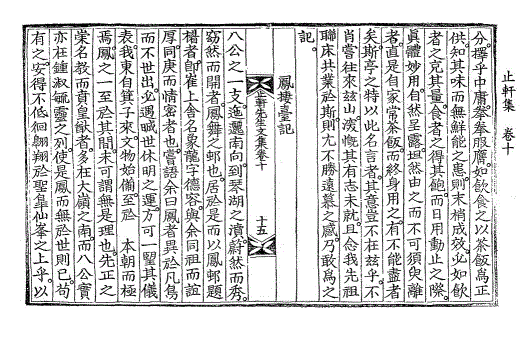 分。择乎中庸。拳拳服膺。如饮食之以茶饭为正供。知其味而无鲜能之患。则末梢成效。必如饮者之充其量。食者之得其饱。而日用动止之际。真体妙用。自然呈露。坦然由之而不可须臾离者。直是自家常茶饭。而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斯亭之特以此名言者。其意岂不在玆乎。不肖尝往来玆山。深慨其有志未就。且念我先祖联床共业于斯。则尤不胜远慕之感。乃敢为之记。
分。择乎中庸。拳拳服膺。如饮食之以茶饭为正供。知其味而无鲜能之患。则末梢成效。必如饮者之充其量。食者之得其饱。而日用动止之际。真体妙用。自然呈露。坦然由之而不可须臾离者。直是自家常茶饭。而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斯亭之特以此名言者。其意岂不在玆乎。不肖尝往来玆山。深慨其有志未就。且念我先祖联床共业于斯。则尤不胜远慕之感。乃敢为之记。凤栖台记
八公之一支。迤逦南向。到琴湖之濆。蔚然而秀。窈然而开者。凤舞之村也。居于是而以凤村题楣者。即崔上舍名象龙字德容。与余同祖而谊厚。同庚而情密者也。尝语余曰凤者异于凡鸟而不世出。必遇晠世休明之运。方可一望其仪表。我东自箕子来。文物始备。至于 本朝而极焉。凤之一至于其间。未可谓无是理也。先正之崇名教而贲皇猷者。多在大岭之南。而八公实亦在钟淑毓灵之列。使是凤而无于世则已。苟有之。安得不低徊翱翔于圣皋仙峰之上乎。以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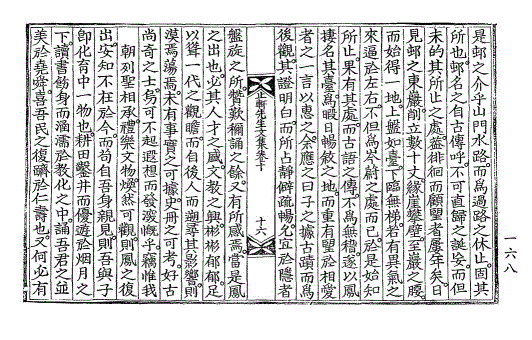 是村之介乎山门水路。而为过路之休止。固其所也。村名之自古传呼。不可直归之诞妄。而但未的其所止之处。盖徘徊而顾望者屡年矣。日见村之东岩。削立数十丈。缘崖攀壁。至岩之腰。而始得一地。上盘如台。下临无梯。若有异气之来逼于左右。不但为岑蔚之处而已。于是始知所止。果有其处。而古语之传。不为无稽。遂以凤栖名其台。为暇日畅叙之地。而重有望于相爱者之一言以惠之。余应之曰子之据古迹而为后观。其證明白。而所占静僻疏畅。允宜于隐者盘旋之所。赞叹称诵之馀。又有所感焉。当是凤之出也。必其人才之盛。文教之兴。彬彬郁郁。足以耸一代之观瞻。而自后人而溯寻其影响。则漠焉荡焉。未有事实之可据。史册之可考。好古尚奇之士。乌可不起遐想而发深慨乎。窃惟我 朝列圣相承。礼乐文物。焕然可观。则凤之复出。安知不在于今。而苟自吾身亲见。则吾与子即化育中一物也。耕田凿井而优游于烟月之下。读书饬身而涵濡于教化之中。诵吾君之并美于尧舜。喜吾民之复跻于仁寿也。又何必有
是村之介乎山门水路。而为过路之休止。固其所也。村名之自古传呼。不可直归之诞妄。而但未的其所止之处。盖徘徊而顾望者屡年矣。日见村之东岩。削立数十丈。缘崖攀壁。至岩之腰。而始得一地。上盘如台。下临无梯。若有异气之来逼于左右。不但为岑蔚之处而已。于是始知所止。果有其处。而古语之传。不为无稽。遂以凤栖名其台。为暇日畅叙之地。而重有望于相爱者之一言以惠之。余应之曰子之据古迹而为后观。其證明白。而所占静僻疏畅。允宜于隐者盘旋之所。赞叹称诵之馀。又有所感焉。当是凤之出也。必其人才之盛。文教之兴。彬彬郁郁。足以耸一代之观瞻。而自后人而溯寻其影响。则漠焉荡焉。未有事实之可据。史册之可考。好古尚奇之士。乌可不起遐想而发深慨乎。窃惟我 朝列圣相承。礼乐文物。焕然可观。则凤之复出。安知不在于今。而苟自吾身亲见。则吾与子即化育中一物也。耕田凿井而优游于烟月之下。读书饬身而涵濡于教化之中。诵吾君之并美于尧舜。喜吾民之复跻于仁寿也。又何必有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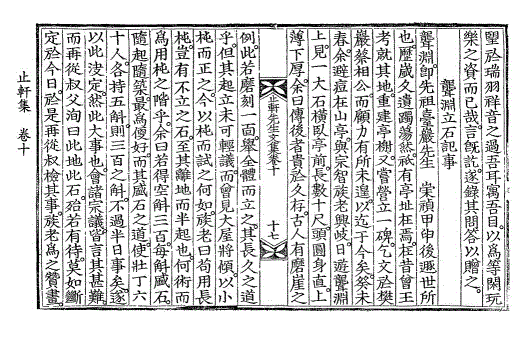 望于瑞羽祥音之过吾耳寓吾目。以为等闲玩乐之资而已哉。言既讫。遂录其问答以赠之。
望于瑞羽祥音之过吾耳寓吾目。以为等闲玩乐之资而已哉。言既讫。遂录其问答以赠之。聋渊立石记事
聋渊。即先祖台岩先生 崇祯甲申后遁世所也。历岁久遗躅荡然。祇有亭址在焉。在昔曾王考就其地。重建亭榭。又尝营立一碑。乞文于樊岩蔡相公。而顾力有所未遑。以迄于今矣。癸未春。余避痘在山亭。与宗智族老兴岐。日游聋渊上。见一大石横卧亭前。长数十尺。头圆身直。上薄下厚。余曰传后者贵于久存。古人有磨崖之例。此若磨刻一面。举全体而立之。其长久之道乎。但其起立未可轻议。而曾见大屋将倾。以小杶而正之。今以杶而试之何如。族老曰苟用长杶。岂有不立之石。至其离地而半起也。何术而为用杶之阶乎。余曰若得空斛三百。每斛盛石。随起随筑。最为便好。而其盛石之道。使壮丁六十人。各持五斛。则三百之斛。不过半日事矣。遂以此决定。然此大事也。会诸宗议。皆言其甚难。而再从叔父洵曰此地此石。殆若有待。莫如断定于今日。于是再从叔检其事。族老为之赞画。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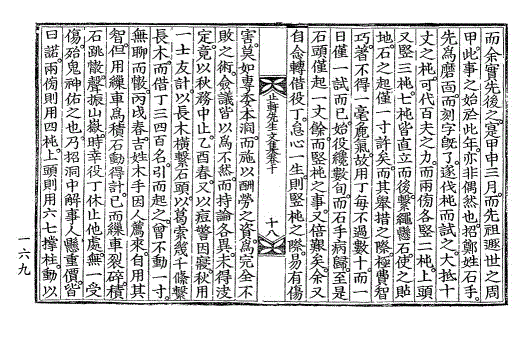 而余实先后之。寔甲申三月。而先祖遁世之用甲。此事之始于此年。亦非偶然也。招郑姓石手。先为磨面。而刻字既了。遂伐杶而试之。大抵十丈之杶。可代百夫之力。而两傍各竖二杶。上头又竖三杶。七杶皆直立而后。系绳悬石。使之贴地。石之起仅一寸许矣。而其举措之际。极费智巧。著不得一毫粗气。故用丁每不过数十。而一日仅一试而已。始役才数旬。而石手病归。至是石头仅起一丈馀。而竖杶之事。又倍艰矣。余又自念转借役丁。怠心一生。则竖杶之际。易有伤害。莫如专委本洞。而施以酬劳之资。为完全不败之术。佥议皆以为不然。而持论各异。未得决定。竟以秋务中止。乙酉春。又以痘警因寝。秋用一士友计。以长木横系石头。以葛索几千绦系长木。而借丁三四百名。引而起之。曾不动一寸。无聊而散。丙戌春。吉姓木手因人荐来。自用其智。但用缫车为积石动得计。已而缫车裂碎。积石跳散。声振山岳。时幸役丁休止他处。无一受伤。殆鬼神佑之也。乃招洞中解事人悬重价。皆曰诺。两傍则用四杶。上头则用六七撑柱。动以
而余实先后之。寔甲申三月。而先祖遁世之用甲。此事之始于此年。亦非偶然也。招郑姓石手。先为磨面。而刻字既了。遂伐杶而试之。大抵十丈之杶。可代百夫之力。而两傍各竖二杶。上头又竖三杶。七杶皆直立而后。系绳悬石。使之贴地。石之起仅一寸许矣。而其举措之际。极费智巧。著不得一毫粗气。故用丁每不过数十。而一日仅一试而已。始役才数旬。而石手病归。至是石头仅起一丈馀。而竖杶之事。又倍艰矣。余又自念转借役丁。怠心一生。则竖杶之际。易有伤害。莫如专委本洞。而施以酬劳之资。为完全不败之术。佥议皆以为不然。而持论各异。未得决定。竟以秋务中止。乙酉春。又以痘警因寝。秋用一士友计。以长木横系石头。以葛索几千绦系长木。而借丁三四百名。引而起之。曾不动一寸。无聊而散。丙戌春。吉姓木手因人荐来。自用其智。但用缫车为积石动得计。已而缫车裂碎。积石跳散。声振山岳。时幸役丁休止他处。无一受伤。殆鬼神佑之也。乃招洞中解事人悬重价。皆曰诺。两傍则用四杶。上头则用六七撑柱。动以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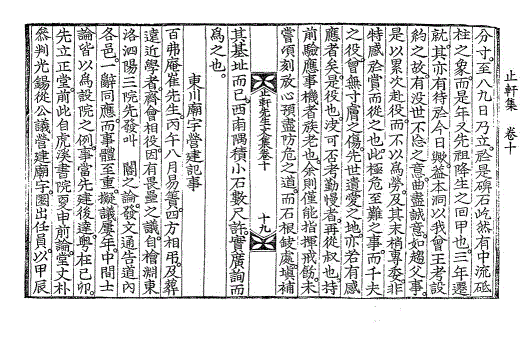 分寸。至八九日乃立。于是碑石屹然有中流砥柱之象。而是年又先祖降生之回甲也。三年迁就。其亦有待于今日欤。盖本洞以我曾王考设约之故。有没世不忘之意。曲尽诚意。如趋父事。是以累次赴役。而不以为劳。及其末梢专委。非特感于赏而从之也。此极危至难之事。而千夫之役。曾无寸肤之伤。先世遗爱之地。亦若有感应者矣。是役也。决可否考勤慢者。再从叔也。持前验应事机者族老也。余则仅能指挥戒饬。未尝顷刻放心预尽防危之道。而石根缺处。填补其基址而已。西南隅积小石数尺许。实广询而为之也。
分寸。至八九日乃立。于是碑石屹然有中流砥柱之象。而是年又先祖降生之回甲也。三年迁就。其亦有待于今日欤。盖本洞以我曾王考设约之故。有没世不忘之意。曲尽诚意。如趋父事。是以累次赴役。而不以为劳。及其末梢专委。非特感于赏而从之也。此极危至难之事。而千夫之役。曾无寸肤之伤。先世遗爱之地。亦若有感应者矣。是役也。决可否考勤慢者。再从叔也。持前验应事机者族老也。余则仅能指挥戒饬。未尝顷刻放心预尽防危之道。而石根缺处。填补其基址而已。西南隅积小石数尺许。实广询而为之也。东川庙宇营建记事
百弗庵崔先生。丙午八月易箦。四方相吊。及葬远近学者。齐会相役。因有畏垒之议。自桧渊东洛泗阳三院先发叫 𨵽之论。发文通告道内各邑。一辞同应。而事体至重。拟议屡年。中间士论皆以为设院之例。事当先建后达。粤在己卯。先立正堂。前此自虎溪书院更申前论。堂丈朴参判光锡从公议营建庙宇。圈出任员。以甲辰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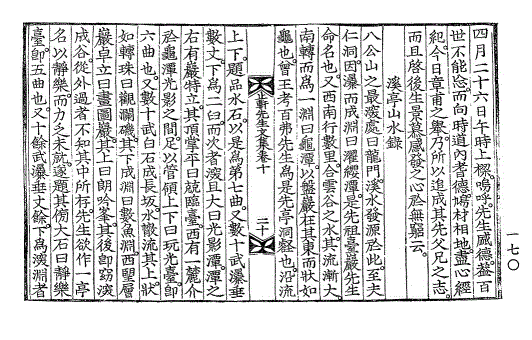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六日午时上梁。呜呼。先生盛德。盖百世不能忘。而向时道内耆德。鸠材相地。尽心经纪。今日章甫之举。乃所以追成其先父兄之志。而且启后生景慕感发之心于无穷云。
四月二十六日午时上梁。呜呼。先生盛德。盖百世不能忘。而向时道内耆德。鸠材相地。尽心经纪。今日章甫之举。乃所以追成其先父兄之志。而且启后生景慕感发之心于无穷云。溪亭山水录
八公山之最深处曰龙门。溪水发源于此。至夫仁洞。因瀑而成渊曰濯缨潭。是先祖台岩先生命名也。又西南行数里。合云谷之水。其流渐大。南转而为一渊曰龟潭。以盘岩在其东而状如龟也。曾王考百弗先生为是先亭洞壑也。沿流上下。题品水石。以是为第七曲。又数十武瀑垂数丈。下为二臼。而次者深且大曰光影潭。潭之右有岩特立。其顶掌平曰兢临台。西有一麓介于龟潭光影之间。足以管领上下曰玩光台。即六曲也。又数十武白石成长坂。水散流其上。状如转珠曰观澜矶。其下成渊曰数鱼渊。西望层岩卓立曰画图岩。其上曰朗吟峰。其后即窈深成谷。从外过者不知其中所存。先生欲作一亭名以静乐。而力乏未就。遂题其傍大石曰静乐台。即五曲也。又十馀武瀑垂丈馀。下为深渊者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1H 页
 二曰愚潭。有大石据乎两间。可坐六七人曰愚石。其西有土坂倚山曰仰高台。其东麓临流宽畅曰风咏台。其下梧柳沿溪曰狎鹭洲。先生尝置小轩其上。名曰静修轩。轩久而圮。未及重刱。即四曲也。又百馀武东折而为聋渊。其北即先祖亭基也。渊上岩石如笼几曰洗心台。前对岩壁削立数丈。面皆粉白曰粉岩。东有微砂遮路成林曰隔尘林。林下馀麓抱溪回蹲曰障川坞。即三曲也。又南折而为渊曰鼓渊。飞瀑驾空。雾雷交腾。水绿如蓝。其深不测。东有石台平衍。先生欲作亭其上。大山名之曰仁智。即二曲也。又其下十馀武水贮成渊曰谷口潭。其东皋曰咏归台。即一曲也。又其下约数矢许有一潭可玩曰涵碧潭。其南又有岩面粉白者。此其洞门而人或称之以白石渡也。盖先生妆点之内。以溪之汇而言则七。通上下二渊而为九曲也。
二曰愚潭。有大石据乎两间。可坐六七人曰愚石。其西有土坂倚山曰仰高台。其东麓临流宽畅曰风咏台。其下梧柳沿溪曰狎鹭洲。先生尝置小轩其上。名曰静修轩。轩久而圮。未及重刱。即四曲也。又百馀武东折而为聋渊。其北即先祖亭基也。渊上岩石如笼几曰洗心台。前对岩壁削立数丈。面皆粉白曰粉岩。东有微砂遮路成林曰隔尘林。林下馀麓抱溪回蹲曰障川坞。即三曲也。又南折而为渊曰鼓渊。飞瀑驾空。雾雷交腾。水绿如蓝。其深不测。东有石台平衍。先生欲作亭其上。大山名之曰仁智。即二曲也。又其下十馀武水贮成渊曰谷口潭。其东皋曰咏归台。即一曲也。又其下约数矢许有一潭可玩曰涵碧潭。其南又有岩面粉白者。此其洞门而人或称之以白石渡也。盖先生妆点之内。以溪之汇而言则七。通上下二渊而为九曲也。北游录
庚午三月初吉。闻外大父立斋先生聚学子设讲于愚山修稧所。乃发向焉。是日宿上枝。再明到长川养真堂。主人之大夫人。即我高王考之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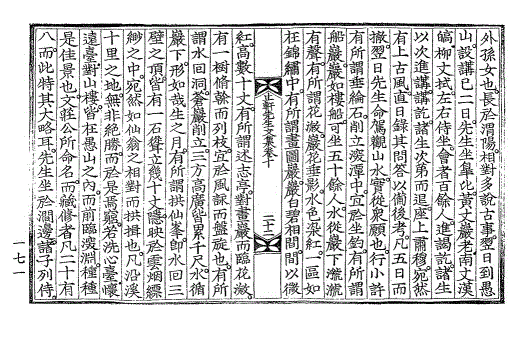 外孙女也。长于渭阳。相对多说古事。翌日到愚山。设讲已二日。先生坐皋比。黄丈岩老,南丈汉皓,柳丈拭。左右侍坐。会者百馀人。进谒讫。诸生以次进讲。讲讫。诸生次第而退。座上肃穆。宛然有上古风。直日录其问答以备后考。凡五日而撤。翌日先生命驾观山水。实从众愿也。行小许有所谓垂纶石。削立深潭中。宜于坐钓。有所谓船岩。岩如楼船。可坐五十馀人。水从岩下㶁㶁有声。有所谓花溆。岩花垂影。水色染红。一区如在锦绣中。有所谓画图岩。岩白碧相间。间以微红。高数十丈。有所谓述志亭。对画岩而临花溆。有一树脩干而列枝。宜于风咏而盘旋也。有所谓水回洞。苍岩削立。三方高广皆累千尺。水循岩下。形如哉生之月。有所谓拱仙峰。即水回三壁之顶。皆有一石耸立几十丈。隐映于云烟缥缈之中。宛然如仙翁之相对而拱揖也。凡沿溪十里之地。无非绝胜。而于是焉穷。若洗心台,怀远台,对山楼。皆在愚山之内。而前临深渊。种种是佳景也。文庄公所命名。而藏修者凡二十有八。而此特其大略耳。先生坐于涧边。诸子列侍。
外孙女也。长于渭阳。相对多说古事。翌日到愚山。设讲已二日。先生坐皋比。黄丈岩老,南丈汉皓,柳丈拭。左右侍坐。会者百馀人。进谒讫。诸生以次进讲。讲讫。诸生次第而退。座上肃穆。宛然有上古风。直日录其问答以备后考。凡五日而撤。翌日先生命驾观山水。实从众愿也。行小许有所谓垂纶石。削立深潭中。宜于坐钓。有所谓船岩。岩如楼船。可坐五十馀人。水从岩下㶁㶁有声。有所谓花溆。岩花垂影。水色染红。一区如在锦绣中。有所谓画图岩。岩白碧相间。间以微红。高数十丈。有所谓述志亭。对画岩而临花溆。有一树脩干而列枝。宜于风咏而盘旋也。有所谓水回洞。苍岩削立。三方高广皆累千尺。水循岩下。形如哉生之月。有所谓拱仙峰。即水回三壁之顶。皆有一石耸立几十丈。隐映于云烟缥缈之中。宛然如仙翁之相对而拱揖也。凡沿溪十里之地。无非绝胜。而于是焉穷。若洗心台,怀远台,对山楼。皆在愚山之内。而前临深渊。种种是佳景也。文庄公所命名。而藏修者凡二十有八。而此特其大略耳。先生坐于涧边。诸子列侍。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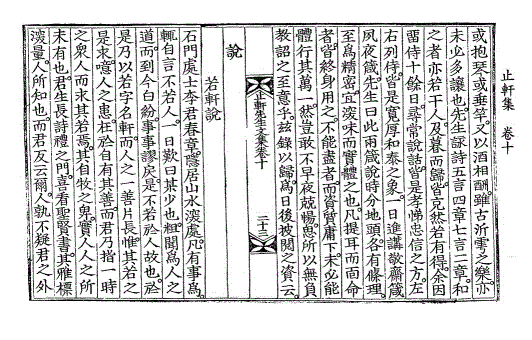 或抱琴或垂竿。又以酒相酬。虽古沂雱之乐。亦未必多让也。先生咏诗五言四章七言二章。和之者亦若干人。及暮而归。皆充然若有得。余因留侍十馀日。寻常说话。皆是孝悌忠信之方。左右列侍。皆是宽厚和泰之象。一日进讲敬斋箴夙夜箴。先生曰此两箴说时分地头。各有条理。至为精密。宜深味而实体之也。凡提耳而面命者。皆终身用之。不能尽者。而资质庸下。未必能体行其万一。然岂敢不早夜兢惕。思所以无负教诏之至意乎。玆录以归。为日后披阅之资云。
或抱琴或垂竿。又以酒相酬。虽古沂雱之乐。亦未必多让也。先生咏诗五言四章七言二章。和之者亦若干人。及暮而归。皆充然若有得。余因留侍十馀日。寻常说话。皆是孝悌忠信之方。左右列侍。皆是宽厚和泰之象。一日进讲敬斋箴夙夜箴。先生曰此两箴说时分地头。各有条理。至为精密。宜深味而实体之也。凡提耳而面命者。皆终身用之。不能尽者。而资质庸下。未必能体行其万一。然岂敢不早夜兢惕。思所以无负教诏之至意乎。玆录以归。为日后披阅之资云。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说
若轩说
石门处士李君春章。隐居山水深处。凡有事为。辄自言不若人。一日叹某少也。粗闻为人之道。而到今白纷。事事谬戾。是不若于人故也。于是乃以若字名轩。而人之一善片长。惟其若之是求。噫人之患。在于自有其善。而君乃指一时之众人而求其若焉。其自牧之卑。实人人之所未有也。君生长诗礼之门。喜看圣贤书。其雅标深量。人所知也。而君反云尔。人孰不疑君之外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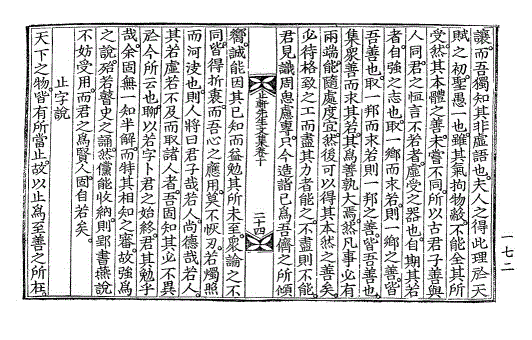 让。而吾独知其非虚语也。夫人之得此理于天赋之初。圣愚一也。虽其气拘物蔽。不能全其所受。然其本体之善。未尝不同。所以古君子善与人同。君之恒言不若者。虚受之器也。自期其若者。自强之志也。取一乡而求若。则一乡之善。皆吾善也。取一邦而求若则一邦之善。皆吾善也。集众善而求其若。其为善孰大焉。然凡事必有两端。能随处度宜。然后可以得其本然之善矣。必待格致之工而尽其力者能之。不尽则不能。君见识周思虑专。只今造诣已为吾侪之所倾向。诚能因其已知而益勉其所未至。众论之不同。皆得折衷。而吾心之应用。莫不恢刃。若烛照而河决也。则人将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其若虚若不及而取诸人者。吾固知其必不异于今所云也。聊以若字卜君之始终。君其勉乎哉。余固无一知半解。而特其相知之审。故强为之说。殆若瞽史之诵。然傥能收纳。则郢书燕说不妨受用。而君之为贤人。固自若矣。
让。而吾独知其非虚语也。夫人之得此理于天赋之初。圣愚一也。虽其气拘物蔽。不能全其所受。然其本体之善。未尝不同。所以古君子善与人同。君之恒言不若者。虚受之器也。自期其若者。自强之志也。取一乡而求若。则一乡之善。皆吾善也。取一邦而求若则一邦之善。皆吾善也。集众善而求其若。其为善孰大焉。然凡事必有两端。能随处度宜。然后可以得其本然之善矣。必待格致之工而尽其力者能之。不尽则不能。君见识周思虑专。只今造诣已为吾侪之所倾向。诚能因其已知而益勉其所未至。众论之不同。皆得折衷。而吾心之应用。莫不恢刃。若烛照而河决也。则人将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其若虚若不及而取诸人者。吾固知其必不异于今所云也。聊以若字卜君之始终。君其勉乎哉。余固无一知半解。而特其相知之审。故强为之说。殆若瞽史之诵。然傥能收纳。则郢书燕说不妨受用。而君之为贤人。固自若矣。止字说
天下之物。皆有所当止。故以止为至善之所在。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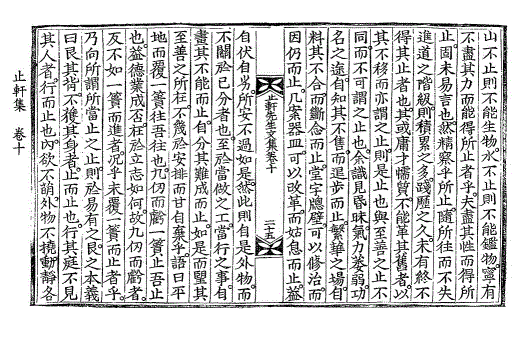 山不止则不能生物。水不止则不能鉴物。宁有不尽其力而能得所止者乎。夫尽其性而得所止。固未易言也。然精察乎所止。随所往而不失进道之阶级。则积累之多。践历之久。未有终不得其止者也。其或庸才懦质。不能革其旧者。以其不移而亦谓之止。则是止也与至善之止不同。而不可谓之止也。余识见昏昧。气力萎弱。功名之途。自知其不售。而退步而止。繁华之场。自料其不合。而断念而止。堂宇窗壁。可以修治。而因仍而止。几案器皿。可以改革。而姑息而止。盖自伏自劣。所安不过如是。然此则自是外物。而不关于己分者也。至于当做之工。当行之事。自画其不能而止。自分其难成而止。如是而望其至善之所在。不几于安排而甘自弃乎。语曰平地而覆一篑往吾往也。九仞而亏一篑止吾止也。盖德业成否。在于立志如何。故九仞而亏者。反不如一篑而进者。况乎未覆一篑而止者乎。乃向所谓所当止之止。则于易有之。艮之本义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内欲不萌。外物不挠。动静各
山不止则不能生物。水不止则不能鉴物。宁有不尽其力而能得所止者乎。夫尽其性而得所止。固未易言也。然精察乎所止。随所往而不失进道之阶级。则积累之多。践历之久。未有终不得其止者也。其或庸才懦质。不能革其旧者。以其不移而亦谓之止。则是止也与至善之止不同。而不可谓之止也。余识见昏昧。气力萎弱。功名之途。自知其不售。而退步而止。繁华之场。自料其不合。而断念而止。堂宇窗壁。可以修治。而因仍而止。几案器皿。可以改革。而姑息而止。盖自伏自劣。所安不过如是。然此则自是外物。而不关于己分者也。至于当做之工。当行之事。自画其不能而止。自分其难成而止。如是而望其至善之所在。不几于安排而甘自弃乎。语曰平地而覆一篑往吾往也。九仞而亏一篑止吾止也。盖德业成否。在于立志如何。故九仞而亏者。反不如一篑而进者。况乎未覆一篑而止者乎。乃向所谓所当止之止。则于易有之。艮之本义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见其人者。行而止也。内欲不萌。外物不挠。动静各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3L 页
 止其所而皆主夫静。其言艮止之义。信乎发其要矣。而惟其知所止得所止之始终本末。盖于大学详且备焉。学者能善读而实体之。持敬而无间断之患。析理而无毫釐之差。则动焉而各止其止。静焉而克止所止。乃得敦艮厚终而为止道之至善矣。前贤之所以开示后学者。不啻丁宁。而反以求诸吾身。则曾无鼓作之勇。又无刻苦之意。光阴浪过。居然已白纷如矣。由前则愚滞蒙昧而未知夫所止。由后则依俙揣量而未得其所止。反复嗟叹之馀。遂书数语。以为馀日之戒云。
止其所而皆主夫静。其言艮止之义。信乎发其要矣。而惟其知所止得所止之始终本末。盖于大学详且备焉。学者能善读而实体之。持敬而无间断之患。析理而无毫釐之差。则动焉而各止其止。静焉而克止所止。乃得敦艮厚终而为止道之至善矣。前贤之所以开示后学者。不啻丁宁。而反以求诸吾身。则曾无鼓作之勇。又无刻苦之意。光阴浪过。居然已白纷如矣。由前则愚滞蒙昧而未知夫所止。由后则依俙揣量而未得其所止。反复嗟叹之馀。遂书数语。以为馀日之戒云。自悔说
余以下愚极陋。析理未精。处事未正。默数平生。愧悔者多。中心不宁。或数月未已。古人虽云悔是向吉者。然留滞在中。实有害于虚静淡平之象。近见外王考时分地头说。略有觉悟。夫事在既往。则言之玷不可为也。行之疵不可追也。只当使吾身亦作彼时分人。不为彼地头事。幡然而改图。奋然而自励。义利公私之间。精察而明辨。使今日时分专属于乾惕而无少间断。今日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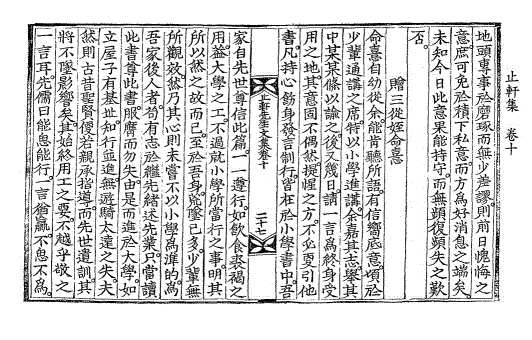 地头专事于磨琢而无少差谬。则前日愧悔之意。庶可免于积下私意。而方为好消息之端矣。未知今日此意果能持守。而无频复频失之叹否。
地头专事于磨琢而无少差谬。则前日愧悔之意。庶可免于积下私意。而方为好消息之端矣。未知今日此意果能持守。而无频复频失之叹否。赠三从侄命憙
命憙自幼从余。能肯听所语。有信向底意。顷于少辈通讲之席。特以小学进讲。余嘉其志。举其中某某条以谕之。后又几日。请一言为终身受用之地。其意固不偶然。提惺之方。不必更引他书。凡持心饬身发言制行。皆在于小学书中。吾家自先世尊信此篇。一一遵行。如饮食裘褐之用。盖大学之工。不过就小学所当行之事。明其所以然之故而已。至于吾身。荒坠已多。少辈无所观效。然乃其心则未尝不以小学为准的。为吾家后人者。苟有志于继先绪述先业。只当读此书尊此书。服膺而勿失。由是而进于大学。如立屋子有基址。知行并进。无游骑太远之失。夫然则古昔圣贤便若亲承指导。而先世遗训。其将不坠影响矣。其始终用工之要。不越乎敬之一言耳。先儒曰能思能行。一言犹赢。不思不为。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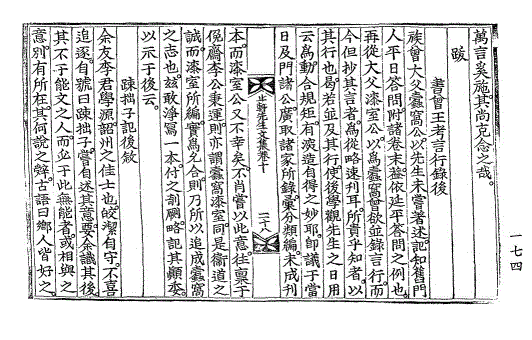 万言奚施。其尚克念之哉。
万言奚施。其尚克念之哉。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跋
书曾王考言行录后
族曾大父蠹窝公。以先生未尝著述。记知旧门人平日答问。附诸卷末。盖依延平答问之例也。再从大父漆室公。以为蠹窝曾欲并录言行。而今但抄其言者。为从略速刊耳。所贵乎知者。以其行也。曷若并及其行。使后学观先生之日用云为。动合规矩。有深造自得之妙耶。即议于当日及门诸公。广取诸家所录。汇分类编。未成刊本。而漆室公又不幸矣。不肖尝以此意。往禀于俛斋李公秉运。则亦谓蠹窝漆室。同是卫道之诚。而漆室所编。实为允合。则乃所以追成蠹窝之志也。玆敢净写一本。付之剞劂。略记其颠委。以示于后云。
疏拙子记后叙
余友李君学源。韶州之佳士也。皎洁自守。不喜追逐。自号曰疏拙子。尝自述其意。要余识其后。其不于能文之人。而必于此无能者。或相与之意。别有所在。其何说之辞。古语曰乡人皆好之。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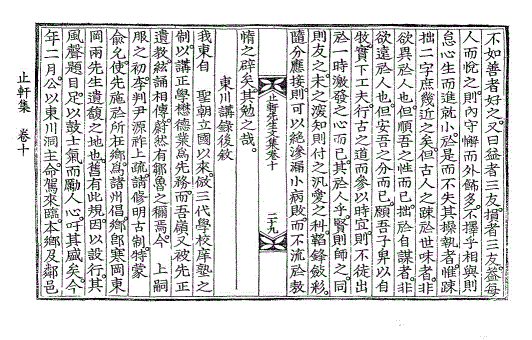 不如善者好之。又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盖每人而悦之。则内守懈而外饰多。不择乎相与则怠心生而进就小。于是而不失其操执者。惟疏拙二字庶几近之矣。但古人之疏于世味者。非欲异于人也。但顺吾之性而已。拙于自谋者。非欲远于人也。但安吾之分而已。愿吾子卑以自牧。实下工夫。行古之道而参以时宜。则不徒出于一时激发之心而已。其于人乎。贤则师之。同则友之。未之深知则付之汎爱之科。韬锋敛彩。随分应接。则可以绝渗漏小病败。而不流于敖惰之辟矣。其勉之哉。
不如善者好之。又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盖每人而悦之。则内守懈而外饰多。不择乎相与则怠心生而进就小。于是而不失其操执者。惟疏拙二字庶几近之矣。但古人之疏于世味者。非欲异于人也。但顺吾之性而已。拙于自谋者。非欲远于人也。但安吾之分而已。愿吾子卑以自牧。实下工夫。行古之道而参以时宜。则不徒出于一时激发之心而已。其于人乎。贤则师之。同则友之。未之深知则付之汎爱之科。韬锋敛彩。随分应接。则可以绝渗漏小病败。而不流于敖惰之辟矣。其勉之哉。东川书堂(저본의 원목차에 근거하여 '书堂'을 보충하였다.)讲录后叙
我东自 圣朝立国以来。仿三代学校庠塾之制。以讲正学懋德业为先务。而吾岭又被先正遗教。弦诵相传。蔚然有邹鲁之称焉。今 上嗣服之初。李判尹源祚上疏。请修明古制。特蒙 俞允。使先施于所在乡。为诸州倡。乡即寒冈东冈两先生遗馥之地也。旧有此规。因以说行。其风声题目。足以鼓士气而励人心。吁其盛矣。今年二月。公以东川洞主。命驾来临。本乡及邻邑
止轩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175L 页
 士林来会者五六十人。咸请讲一经。以备故事。公要余同。令诸生相揖讫。进讲大学。至日暮而罢。此曾王考讲道之所也。近年以来讲说寥寥。赖公一出。使古道复明于今日。岂非幸欤。况此异言喧豗。 朝家之诛讨方严。而使一方之士。因是而有感发兴起之效。则是公之志也。但以岁歉财匮。不能多日周旋。极意论辨。是可恨耳。判尹公临归。属余一言以识。遂忘拙书其事如右。
士林来会者五六十人。咸请讲一经。以备故事。公要余同。令诸生相揖讫。进讲大学。至日暮而罢。此曾王考讲道之所也。近年以来讲说寥寥。赖公一出。使古道复明于今日。岂非幸欤。况此异言喧豗。 朝家之诛讨方严。而使一方之士。因是而有感发兴起之效。则是公之志也。但以岁歉财匮。不能多日周旋。极意论辨。是可恨耳。判尹公临归。属余一言以识。遂忘拙书其事如右。书溪亭眉叟先生篆额后
右眉叟许文正公遗墨也。先祖台岩府君。与文正公有同门之谊。由今日溯寻遗响。只此四字在焉。玆以刻揭亭楣。以为寓慕之地云尔。台岩后孙孝述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