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x 页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
序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299H 页
 续性理大全序
续性理大全序道也者。原于天者也。性也者。命于物者也。理也者。性之真而道之实然者也。盖自天道流亨。人受其中。莫善于性而发之情则或荡而凿。莫尊于理而囿于气则或掩而微。穷理尽性。以行其道。斯之谓尽人。人惟一心。虚灵洞澈。该理气而统性情。广大侔天地。神明合鬼神。所谓万化皆从心出也。治心得其方则性命于理。治心不得其方则性命于气。理气之相胜而性之全不全可知也。自夫精一之传。中极之建。固已穷探性理之原。而孔门既罕言之。故学者有不得而闻者。洛建以来。为人转切。于是乎极本穷源。将以阐命性之原。发理气之键。其为言不一。而要皆所以为治心之妙方。复性之指南。正如耒耟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备者矣。此永乐诸儒所以编辑为书。目之为性理大全。而斯道于是乎在矣。吾东方自父师以来。固已与闻乎皇极敷言之教。而若其折衷前言。准的百代。至我老先生而尤大焉。其为言一皆本之以六经。参之以洛建。蚕毛之微。命性之原。剖析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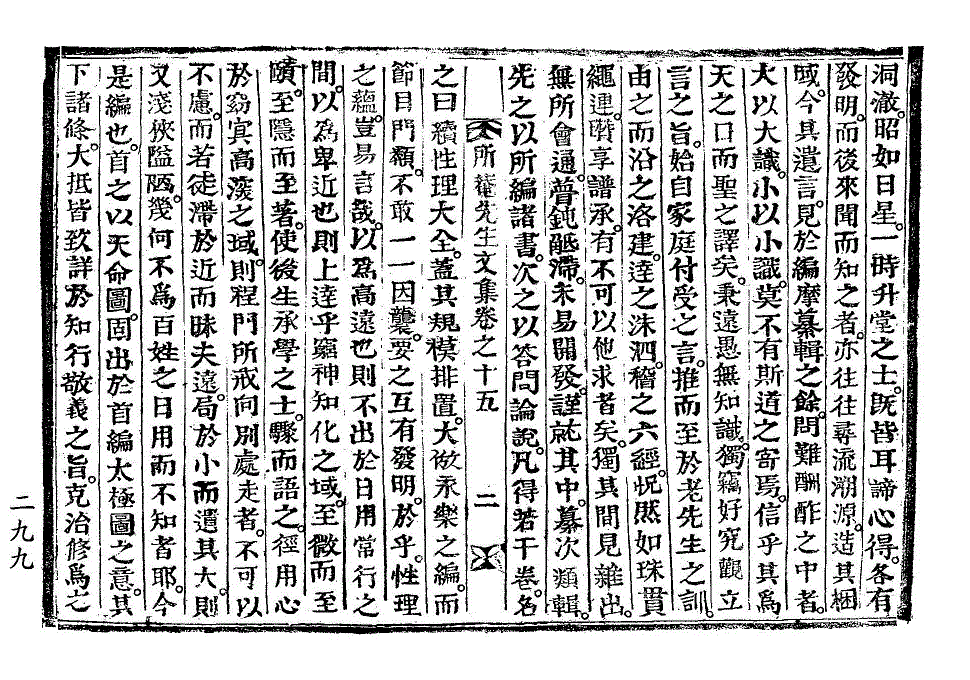 洞澈。昭如日星。一时升堂之士。既皆耳谛心得。各有发明。而后来闻而知之者。亦往往寻流溯源。造其梱域。今其遗言。见于编摩纂辑之馀。问难酬酢之中者。大以大识。小以小识。莫不有斯道之寄焉。信乎其为天之口而圣之译矣。秉远愚无知识。独窃好究观立言之旨。始自家庭付受之言。推而至于老先生之训。由之而沿之洛建。达之洙泗。稽之六经。恍然如珠贯绳连。瓒享谱承。有不可以他求者矣。独其间见杂出。无所会通。瞢钝抵滞。未易开发。谨就其中。纂次类辑。先之以所编诸书。次之以答问论说。凡得若干卷。名之曰续性理大全。盖其规模排置。大仿永乐之编。而节目门类。不敢一一因袭。要之互有发明。于乎。性理之蕴。岂易言哉。以为高远也则不出于日用常行之间。以为卑近也则上达乎穷神知化之域。至微而至赜。至隐而至著。使后生承学之士。骤而语之。径用心于窈冥高深之域。则程门所戒向别处走者。不可以不虑。而若徒滞于近而昧夫远。局于小而遗其大。则又浅狭隘陋。几何不为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耶。今是编也。首之以天命图。固出于首编太极图之意。其下诸条。大抵皆致详于知行敬义之旨。克治修为之
洞澈。昭如日星。一时升堂之士。既皆耳谛心得。各有发明。而后来闻而知之者。亦往往寻流溯源。造其梱域。今其遗言。见于编摩纂辑之馀。问难酬酢之中者。大以大识。小以小识。莫不有斯道之寄焉。信乎其为天之口而圣之译矣。秉远愚无知识。独窃好究观立言之旨。始自家庭付受之言。推而至于老先生之训。由之而沿之洛建。达之洙泗。稽之六经。恍然如珠贯绳连。瓒享谱承。有不可以他求者矣。独其间见杂出。无所会通。瞢钝抵滞。未易开发。谨就其中。纂次类辑。先之以所编诸书。次之以答问论说。凡得若干卷。名之曰续性理大全。盖其规模排置。大仿永乐之编。而节目门类。不敢一一因袭。要之互有发明。于乎。性理之蕴。岂易言哉。以为高远也则不出于日用常行之间。以为卑近也则上达乎穷神知化之域。至微而至赜。至隐而至著。使后生承学之士。骤而语之。径用心于窈冥高深之域。则程门所戒向别处走者。不可以不虑。而若徒滞于近而昧夫远。局于小而遗其大。则又浅狭隘陋。几何不为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耶。今是编也。首之以天命图。固出于首编太极图之意。其下诸条。大抵皆致详于知行敬义之旨。克治修为之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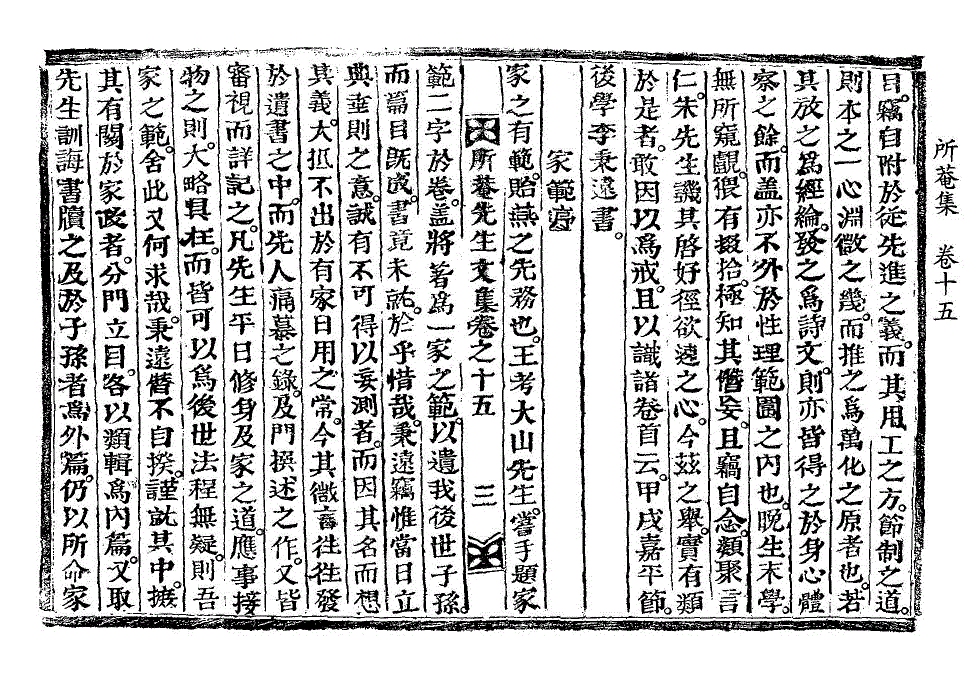 目。窃自附于从先进之义。而其用工之方。节制之道。则本之一心渊微之几。而推之为万化之原者也。若其放之为经纶。发之为诗文。则亦皆得之于身心体察之馀。而盖亦不外于性理范围之内也。晚生末学。无所窥觑。猥有掇拾。极知其僭妄。且窃自念。类聚言仁。朱先生讥其启好径欲速之心。今兹之举。实有类于是者。敢因以为戒。且以识诸卷首云。甲戌嘉平节。后学李秉远书。
目。窃自附于从先进之义。而其用工之方。节制之道。则本之一心渊微之几。而推之为万化之原者也。若其放之为经纶。发之为诗文。则亦皆得之于身心体察之馀。而盖亦不外于性理范围之内也。晚生末学。无所窥觑。猥有掇拾。极知其僭妄。且窃自念。类聚言仁。朱先生讥其启好径欲速之心。今兹之举。实有类于是者。敢因以为戒。且以识诸卷首云。甲戌嘉平节。后学李秉远书。家范序
家之有范。贻燕之先务也。王考大山先生。尝手题家范二字于卷。盖将著为一家之范。以遗我后世子孙。而篇目既成。书竟未就。于乎惜哉。秉远窃惟当日立典垂则之意。诚有不可得以妄测者。而因其名而想其义。大抵不出于有家日用之常。今其微言往往发于遗书之中。而先人痛慕之录。及门撰述之作。又皆审视而详记之。凡先生平日修身及家之道。应事接物之则。大略具在。而皆可以为后世法程无疑。则吾家之范。舍此又何求哉。秉远僭不自揆。谨就其中。摭其有关于家政者。分门立目。各以类辑为内篇。又取先生训诲书牍之及于子孙者为外篇。仍以所命家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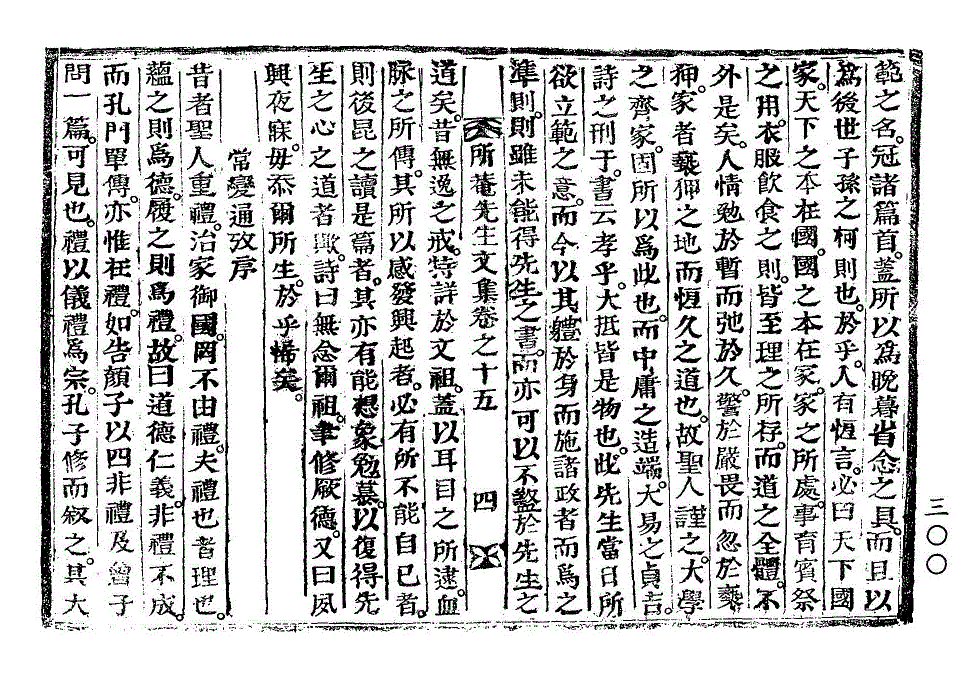 范之名。冠诸篇首。盖所以为晚暮省念之具。而且以为后世子孙之柯则也。于乎。人有恒言。必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所处。事育宾祭之用。衣服饮食之则。皆至理之所存。而道之全体。不外是矣。人情勉于暂而弛于久。警于严畏而忽于亵狎。家者亵狎之地而恒久之道也。故圣人谨之。大学之齐家。固所以为此也。而中庸之造端。大易之贞吉。诗之刑于。书云孝乎。大抵皆是物也。此先生当日所欲立范之意。而今以其体于身而施诸政者而为之准则。则虽未能得先生之书。而亦可以不盭于先生之道矣。昔无逸之戒。特详于文祖。盖以耳目之所逮。血脉之所传。其所以感发兴起者。必有所不能自已者。则后昆之读是篇者。其亦有能想象勉慕。以复得先生之心之道者欤。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于乎悕矣。
范之名。冠诸篇首。盖所以为晚暮省念之具。而且以为后世子孙之柯则也。于乎。人有恒言。必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所处。事育宾祭之用。衣服饮食之则。皆至理之所存。而道之全体。不外是矣。人情勉于暂而弛于久。警于严畏而忽于亵狎。家者亵狎之地而恒久之道也。故圣人谨之。大学之齐家。固所以为此也。而中庸之造端。大易之贞吉。诗之刑于。书云孝乎。大抵皆是物也。此先生当日所欲立范之意。而今以其体于身而施诸政者而为之准则。则虽未能得先生之书。而亦可以不盭于先生之道矣。昔无逸之戒。特详于文祖。盖以耳目之所逮。血脉之所传。其所以感发兴起者。必有所不能自已者。则后昆之读是篇者。其亦有能想象勉慕。以复得先生之心之道者欤。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于乎悕矣。常变通考序
昔者圣人重礼。治家御国。罔不由礼。夫礼也者理也。蕴之则为德。履之则为礼。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而孔门单传。亦惟在礼。如告颜子以四非礼及曾子问一篇。可见也。礼以仪礼为宗。孔子修而叙之。其大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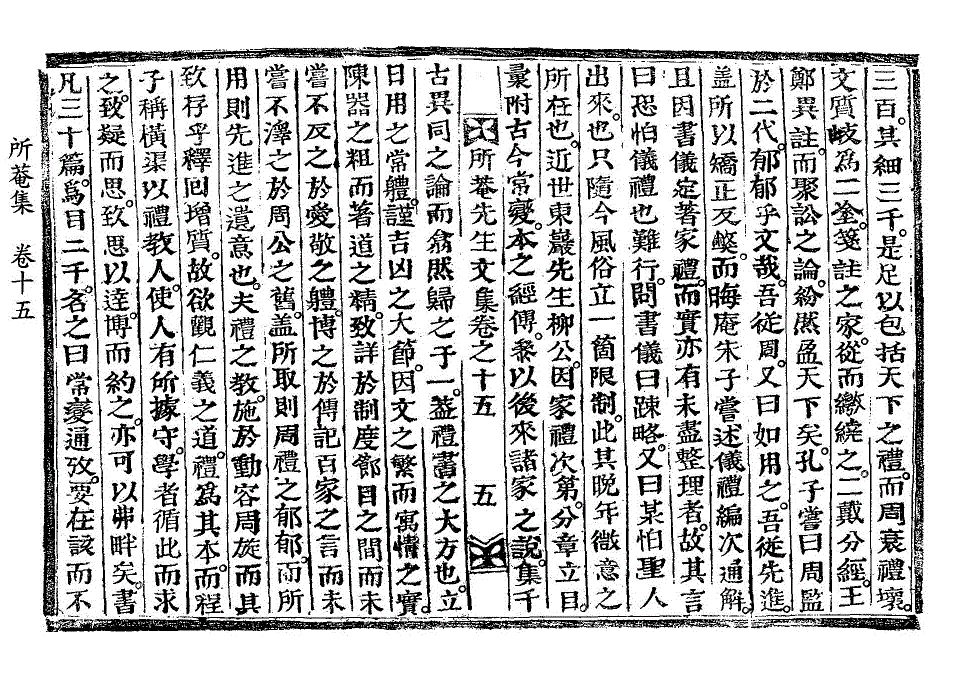 三百。其细三千。是足以包括天下之礼。而周衰礼坏。文质歧为二涂。笺注之家。从而缴绕之。二戴分经。王郑异注。而聚讼之论。纷然盈天下矣。孔子尝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如用之。吾从先进。盖所以矫正反弊。而晦庵朱子尝述仪礼编次通解。且因书仪定著家礼。而实亦有未尽整理者。故其言曰恐怕仪礼也难行。问书仪曰疏略。又曰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此其晚年微意之所在也。近世东岩先生柳公。因家礼次第。分章立目。汇附古今常变。本之经传。参以后来诸家之说。集千古异同之论而翕然归之于一。盖礼书之大方也。立日用之常体。谨吉凶之大节。因文之繁而寓情之实。陈器之粗而著道之精。致详于制度节目之间而未尝不反之于爱敬之体。博之于传记百家之言而未尝不泽之于周公之旧。盖所取则周礼之郁郁。而所用则先进之遗意也。夫礼之教。施于动容周旋而其致存乎释回增质。故欲观仁义之道。礼为其本。而程子称横渠以礼教人。使人有所据守。学者循此而求之。致疑而思。致思以达。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矣。书凡三十篇。为目二千。名之曰常变通考。要在该而不
三百。其细三千。是足以包括天下之礼。而周衰礼坏。文质歧为二涂。笺注之家。从而缴绕之。二戴分经。王郑异注。而聚讼之论。纷然盈天下矣。孔子尝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如用之。吾从先进。盖所以矫正反弊。而晦庵朱子尝述仪礼编次通解。且因书仪定著家礼。而实亦有未尽整理者。故其言曰恐怕仪礼也难行。问书仪曰疏略。又曰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此其晚年微意之所在也。近世东岩先生柳公。因家礼次第。分章立目。汇附古今常变。本之经传。参以后来诸家之说。集千古异同之论而翕然归之于一。盖礼书之大方也。立日用之常体。谨吉凶之大节。因文之繁而寓情之实。陈器之粗而著道之精。致详于制度节目之间而未尝不反之于爱敬之体。博之于传记百家之言而未尝不泽之于周公之旧。盖所取则周礼之郁郁。而所用则先进之遗意也。夫礼之教。施于动容周旋而其致存乎释回增质。故欲观仁义之道。礼为其本。而程子称横渠以礼教人。使人有所据守。学者循此而求之。致疑而思。致思以达。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矣。书凡三十篇。为目二千。名之曰常变通考。要在该而不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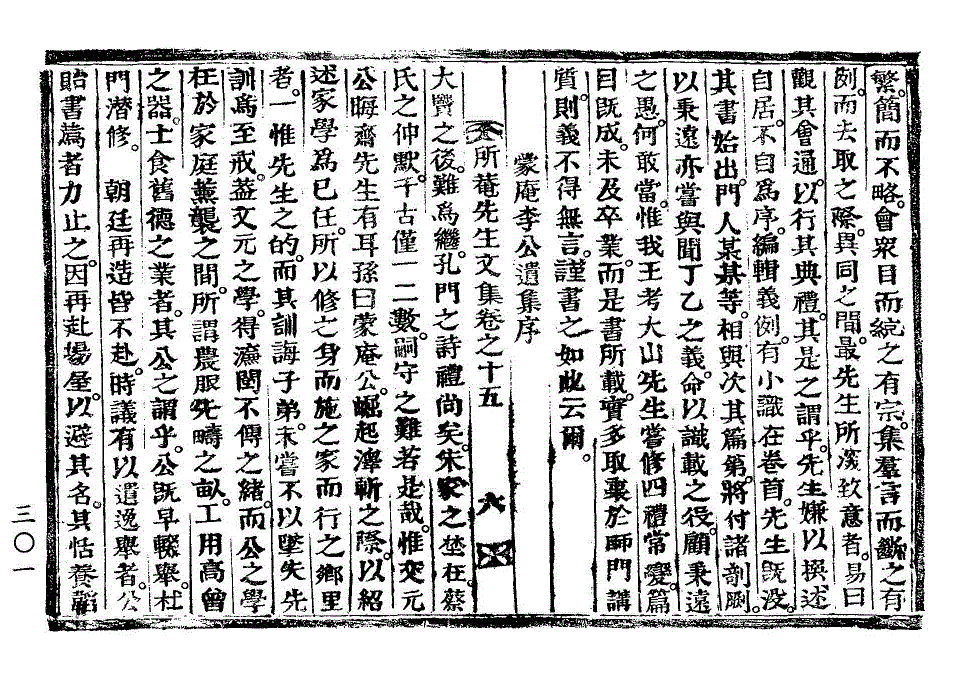 繁。简而不略。会众目而统之有宗。集群言而断之有例。而去取之际。异同之间。最先生所深致意者。易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其是之谓乎。先生嫌以撰述自居。不自为序。编辑义例。有小识在卷首。先生既没。其书始出。门人某某等。相与次其篇第。将付诸剞劂。以秉远亦尝与闻丁乙之义。命以识载之役。顾秉远之愚。何敢当。惟我王考大山先生尝修四礼常变。篇目既成。未及卒业。而是书所载。实多取衷于师门讲质。则义不得无言。谨书之如此云尔。
繁。简而不略。会众目而统之有宗。集群言而断之有例。而去取之际。异同之间。最先生所深致意者。易曰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其是之谓乎。先生嫌以撰述自居。不自为序。编辑义例。有小识在卷首。先生既没。其书始出。门人某某等。相与次其篇第。将付诸剞劂。以秉远亦尝与闻丁乙之义。命以识载之役。顾秉远之愚。何敢当。惟我王考大山先生尝修四礼常变。篇目既成。未及卒业。而是书所载。实多取衷于师门讲质。则义不得无言。谨书之如此云尔。蒙庵李公遗集序
大贤之后。难为继。孔门之诗礼尚矣。朱家之野在。蔡氏之仲默。千古仅一二数。嗣守之难若是哉。惟文元公晦斋先生有耳孙曰蒙庵公。崛起泽斩之际。以绍述家学为己任。所以修之身而施之家而行之乡里者。一惟先生之的。而其训诲子弟。未尝不以坠失先训为至戒。盖文元之学。得濂闽不传之绪。而公之学在于家庭薰袭之间。所谓农服先畴之亩。工用高曾之器。士食旧德之业者。其公之谓乎。公既早辍举。杜门潜修。 朝廷再造皆不赴。时议有以遗逸举者。公贻书荐者力止之。因再赴场屋。以避其名。其恬养韬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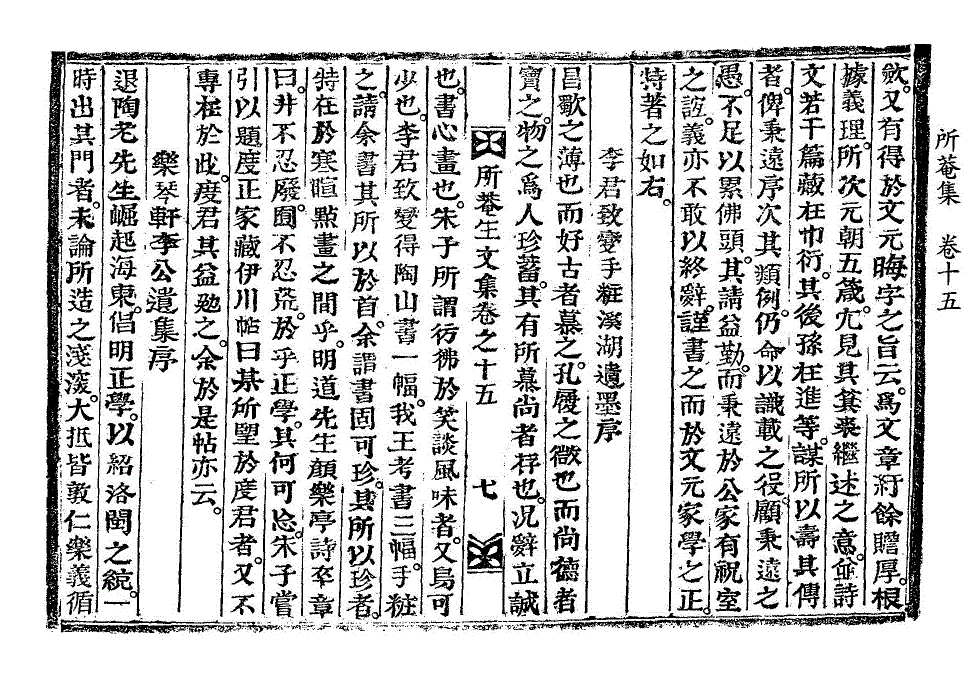 敛。又有得于文元晦字之旨云。为文章纡馀赡厚。根据义理。所次元朝五箴。尤见其箕裘继述之意。并诗文若干篇藏在巾衍。其后孙在进等。谋所以寿其传者。俾秉远序次其类例。仍命以识载之役。顾秉远之愚。不足以累佛头。其请益勤。而秉远于公家有祝室之谊。义亦不敢以终辞。谨书之而于文元家学之正。特著之如右。
敛。又有得于文元晦字之旨云。为文章纡馀赡厚。根据义理。所次元朝五箴。尤见其箕裘继述之意。并诗文若干篇藏在巾衍。其后孙在进等。谋所以寿其传者。俾秉远序次其类例。仍命以识载之役。顾秉远之愚。不足以累佛头。其请益勤。而秉远于公家有祝室之谊。义亦不敢以终辞。谨书之而于文元家学之正。特著之如右。李君致燮手妆溪湖遗墨序
昌歜之薄也而好古者慕之。孔履之微也而尚德者宝之。物之为人珍蓄。其有所慕尚者存也。况辞立诚也。书心画也。朱子所谓彷佛于笑谈风味者。又乌可少也。李君致燮得陶山书一幅。我王考书三幅。手妆之。请余书其所以于首。余谓书固可珍。其所以珍者。特在于寒暄点画之间乎。明道先生颜乐亭诗卒章曰。井不忍废。囿不忍荒。于乎正学。其何可忘。朱子尝引以题度正家藏伊川帖曰某所望于度君者。又不专在于此。度君其益勉之。余于是帖亦云。
乐琴轩李公遗集序
退陶老先生崛起海东。倡明正学。以绍洛闽之统。一时出其门者。未论所造之浅深。大抵皆敦仁乐义循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2L 页
 蹈规矩。恂恂有君子之风。况于家庭濡染之教乎。惟我乐琴轩李公。实先生袒免之孙也。亦尝得逮于先生之世。曾蒙抚顶之爱。书进忠孝二字。大被奖与之化。盖其发端启键于幼稚之时者如此。及稍长。内则与伯氏松涧公为天伦知己。外则与鹤峰金先生为表从兄弟。出入薰袭。皆陶山旨诀也。尝喟然曰生大贤之门而抱生晚之叹。惟有讲明遗绪。以不坠家学耳。与及门诸先达。讨论遗书。考校整釐。除问寝视膳外。净扫一室。左右图书。惟见此事之独大也。公年十一。守先公制。居庐终三年。逮壬辰岛夷之乱。以一介书生。雪涕登坛。纠合义旅。慨然有削平之志。尝有诗曰君雠未报身犹在。举目山河不尽羞。又尝临阵誓众曰书生胆气。只当为国一死。盖公为亲则守庐墓之制。为国而效敌忾之义。即龆龀所书进于先生者。盖若为之兆者。而先生所以奖诩而期勉之者。其必有以知公之能办此矣。公晚除寝郎不起。就宅南辟小斋。扁以乐琴轩。日啸傲其中。与申梧峰,白惺轩,崔讱斋诸公。讲论切磋。结以道义。想其往复质卞之间。必多有可传者。而今皆散佚无徵。独有唱酬若干首。不足以尽公之蕴。然冲淡萧散之味。激昂慷慨之作。皆
蹈规矩。恂恂有君子之风。况于家庭濡染之教乎。惟我乐琴轩李公。实先生袒免之孙也。亦尝得逮于先生之世。曾蒙抚顶之爱。书进忠孝二字。大被奖与之化。盖其发端启键于幼稚之时者如此。及稍长。内则与伯氏松涧公为天伦知己。外则与鹤峰金先生为表从兄弟。出入薰袭。皆陶山旨诀也。尝喟然曰生大贤之门而抱生晚之叹。惟有讲明遗绪。以不坠家学耳。与及门诸先达。讨论遗书。考校整釐。除问寝视膳外。净扫一室。左右图书。惟见此事之独大也。公年十一。守先公制。居庐终三年。逮壬辰岛夷之乱。以一介书生。雪涕登坛。纠合义旅。慨然有削平之志。尝有诗曰君雠未报身犹在。举目山河不尽羞。又尝临阵誓众曰书生胆气。只当为国一死。盖公为亲则守庐墓之制。为国而效敌忾之义。即龆龀所书进于先生者。盖若为之兆者。而先生所以奖诩而期勉之者。其必有以知公之能办此矣。公晚除寝郎不起。就宅南辟小斋。扁以乐琴轩。日啸傲其中。与申梧峰,白惺轩,崔讱斋诸公。讲论切磋。结以道义。想其往复质卞之间。必多有可传者。而今皆散佚无徵。独有唱酬若干首。不足以尽公之蕴。然冲淡萧散之味。激昂慷慨之作。皆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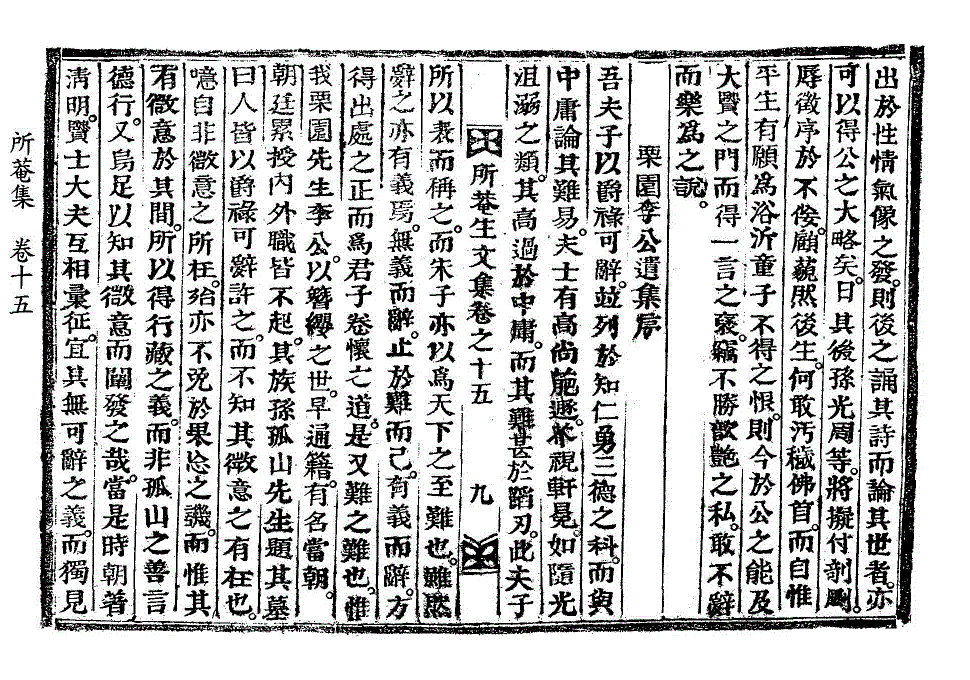 出于性情气像之发。则后之诵其诗而论其世者。亦可以得公之大略矣。日其后孙光周等。将拟付剞劂。辱徵序于不佞。顾藐然后生。何敢污秽佛首。而自惟平生有愿为浴沂童子不得之恨。则今于公之能及大贤之门而得一言之褒。窃不胜歆艳之私。敢不辞而乐为之说。
出于性情气像之发。则后之诵其诗而论其世者。亦可以得公之大略矣。日其后孙光周等。将拟付剞劂。辱徵序于不佞。顾藐然后生。何敢污秽佛首。而自惟平生有愿为浴沂童子不得之恨。则今于公之能及大贤之门而得一言之褒。窃不胜歆艳之私。敢不辞而乐为之说。栗园李公遗集序
吾夫子以爵禄可辞。并列于知仁勇三德之科。而与中庸论其难易。夫士有高尚萉遁。芥视轩冕。如随光沮溺之类。其高过于中庸。而其难甚于蹈刃。此夫子所以表而称之。而朱子亦以为天下之至难也。虽然辞之亦有义焉。无义而辞。止于难而已。有义而辞。方得出处之正而为君子卷怀之道。是又难之难也。惟我栗园先生李公。以簪缨之世。早通籍。有名当朝。 朝廷累授内外职皆不起。其族孙孤山先生题其墓曰人皆以爵禄可辞许之。而不知其微意之有在也。噫自非微意之所在。殆亦不免于果忘之讥。而惟其有微意于其间。所以得行藏之义。而非孤山之善言德行。又乌足以知其微意而阐发之哉。当是时朝著清明。贤士大夫互相汇征。宜其无可辞之义。而独见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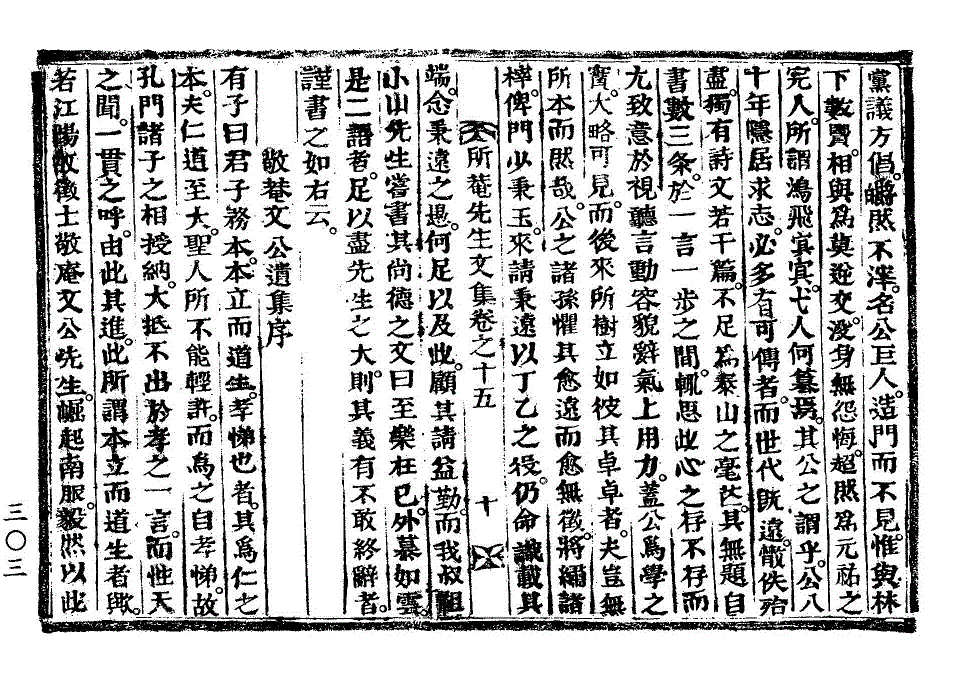 党议方倡。皭然不滓。名公巨人。造门而不见。惟与林下数贤。相与为莫逆交。没身无怨悔。超然为元祐之完人。所谓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其公之谓乎。公八十年隐居求志。必多有可传者。而世代既远。散佚殆尽。独有诗文若干篇。不足为泰山之毫芒。其无题自书数三条。于一言一步之间。辄思此心之存不存而尤致意于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用力。盖公为学之实。大略可见。而后来所树立如彼其卓卓者。夫岂无所本而然哉。公之诸孙惧其愈远而愈无徵。将绣诸梓。俾门少秉玉。来请秉远以丁乙之役。仍命识载其端。念秉远之愚。何足以及此。顾其请益勤。而我叔祖小山先生尝书其尚德之文曰至乐在己。外慕如云。是二语者。足以尽先生之大。则其义有不敢终辞者。谨书之如右云。
党议方倡。皭然不滓。名公巨人。造门而不见。惟与林下数贤。相与为莫逆交。没身无怨悔。超然为元祐之完人。所谓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其公之谓乎。公八十年隐居求志。必多有可传者。而世代既远。散佚殆尽。独有诗文若干篇。不足为泰山之毫芒。其无题自书数三条。于一言一步之间。辄思此心之存不存而尤致意于视听言动容貌辞气上用力。盖公为学之实。大略可见。而后来所树立如彼其卓卓者。夫岂无所本而然哉。公之诸孙惧其愈远而愈无徵。将绣诸梓。俾门少秉玉。来请秉远以丁乙之役。仍命识载其端。念秉远之愚。何足以及此。顾其请益勤。而我叔祖小山先生尝书其尚德之文曰至乐在己。外慕如云。是二语者。足以尽先生之大。则其义有不敢终辞者。谨书之如右云。敬庵文公遗集序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夫仁道至大。圣人所不能轻许。而为之自孝悌。故孔门诸子之相授纳。大抵不出于孝之一言。而性天之闻。一贯之呼。由此其进。此所谓本立而道生者欤。若江阳故徵士敬庵文公先生。崛起南服。毅然以此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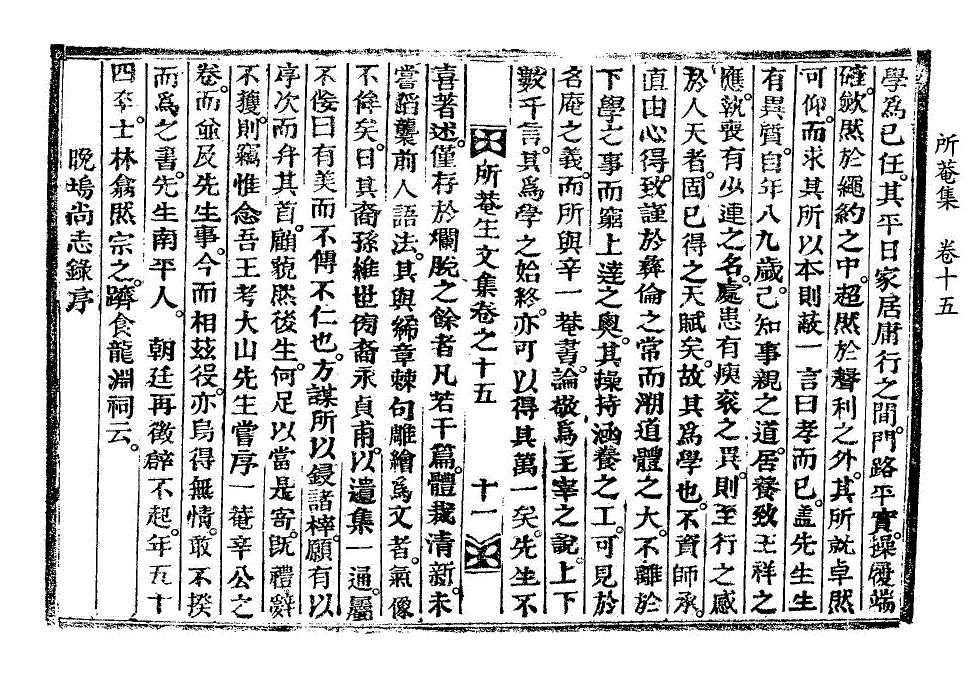 学为己任。其平日家居庸行之间。门路平实。操履端确。敛然于绳约之中。超然于声利之外。其所就卓然可仰。而求其所以本则蔽一言曰孝而已。盖先生生有异质。自年八九岁。已知事亲之道。居养致王祥之应。执丧有少连之名。处患有庾衮之异。则至行之感于人天者。固已得之天赋矣。故其为学也。不资师承。直由心得。致谨于彝伦之常而溯道体之大。不离于下学之事而穷上达之奥。其操持涵养之工。可见于名庵之义。而所与辛一庵书。论敬为主宰之说。上下数千言。其为学之始终。亦可以得其万一矣。先生不喜著述。仅存于烂脱之馀者凡若干篇。体裁清新。未尝蹈袭前人语法。其与絺章棘句雕绘为文者。气像不侔矣。日其裔孙维世傍裔永贞甫。以遗集一通。属不佞曰有美而不传不仁也。方谋所以锓诸梓。愿有以序次而弁其首。顾藐然后生。何足以当是寄。既礼辞不获。则窃惟念吾王考大山先生尝序一庵辛公之卷。而并及先生事。今而相兹役。亦乌得无情。敢不揆而为之书。先生南平人。 朝廷再徵辟不起。年五十四卒。士林翕然宗之。跻食龙渊祠云。
学为己任。其平日家居庸行之间。门路平实。操履端确。敛然于绳约之中。超然于声利之外。其所就卓然可仰。而求其所以本则蔽一言曰孝而已。盖先生生有异质。自年八九岁。已知事亲之道。居养致王祥之应。执丧有少连之名。处患有庾衮之异。则至行之感于人天者。固已得之天赋矣。故其为学也。不资师承。直由心得。致谨于彝伦之常而溯道体之大。不离于下学之事而穷上达之奥。其操持涵养之工。可见于名庵之义。而所与辛一庵书。论敬为主宰之说。上下数千言。其为学之始终。亦可以得其万一矣。先生不喜著述。仅存于烂脱之馀者凡若干篇。体裁清新。未尝蹈袭前人语法。其与絺章棘句雕绘为文者。气像不侔矣。日其裔孙维世傍裔永贞甫。以遗集一通。属不佞曰有美而不传不仁也。方谋所以锓诸梓。愿有以序次而弁其首。顾藐然后生。何足以当是寄。既礼辞不获。则窃惟念吾王考大山先生尝序一庵辛公之卷。而并及先生事。今而相兹役。亦乌得无情。敢不揆而为之书。先生南平人。 朝廷再徵辟不起。年五十四卒。士林翕然宗之。跻食龙渊祠云。晚坞尚志录序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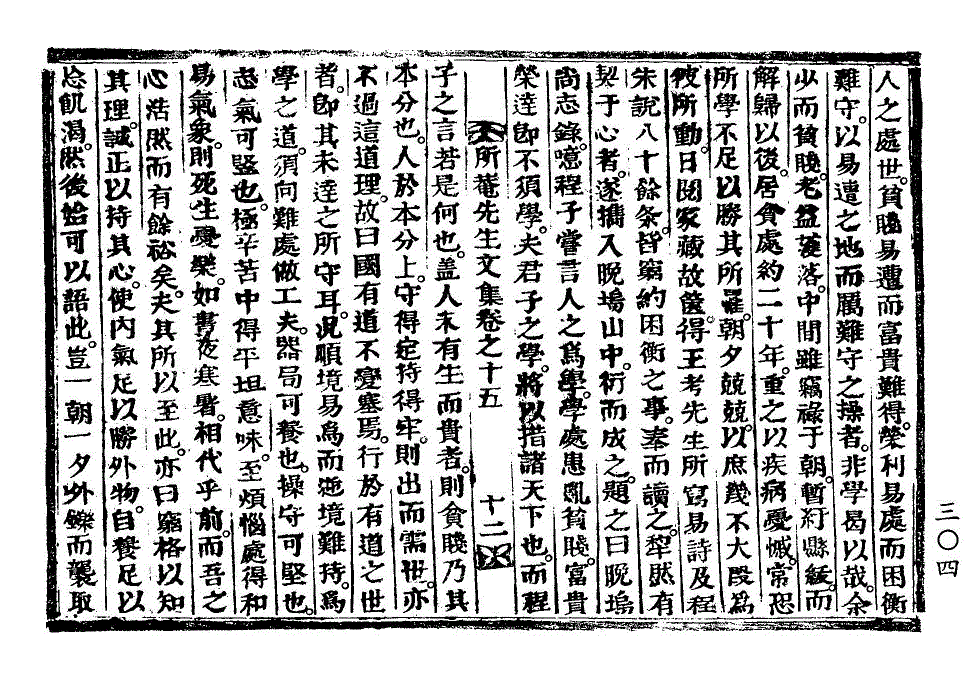 人之处世。贫贱易遭而富贵难得。荣利易处而困衡难守。以易遭之地而厉难守之操者。非学曷以哉。余少而贫贱。老益濩落。中间虽窃禄于朝。暂纡县绂。而解归以后。居贫处约二十年。重之以疾病忧戚。常恐所学不足以胜其所罹。朝夕兢兢。以庶几不大段为彼所动。日阅家藏故箧。得王考先生所写易诗及程朱说八十馀条。皆穷约困衡之事。奉而读之。犁然有契于心者。遂携入晚坞山中。衍而成之。题之曰晚坞尚志录。噫程子尝言人之为学。学处患乱贫贱。富贵荣达即不须学。夫君子之学。将以措诸天下也。而程子之言若是何也。盖人未有生而贵者。则贫贱乃其本分也。人于本分上。守得定持得牢。则出而需世。亦不过这道理。故曰国有道不变塞焉。行于有道之世者。即其未达之所守耳。况顺境易为而逆境难持。为学之道。须向难处做工夫。器局可养也。操守可坚也。志气可竖也。极辛苦中得平坦意味。至烦恼处得和易气象。则死生忧乐。如昼夜寒暑。相代乎前。而吾之心浩然而有馀裕矣。夫其所以至此。亦曰穷格以知其理。诚正以持其心。使内气足以胜外物。自养足以忘饥渴。然后始可以语此。岂一朝一夕外铄而袭取
人之处世。贫贱易遭而富贵难得。荣利易处而困衡难守。以易遭之地而厉难守之操者。非学曷以哉。余少而贫贱。老益濩落。中间虽窃禄于朝。暂纡县绂。而解归以后。居贫处约二十年。重之以疾病忧戚。常恐所学不足以胜其所罹。朝夕兢兢。以庶几不大段为彼所动。日阅家藏故箧。得王考先生所写易诗及程朱说八十馀条。皆穷约困衡之事。奉而读之。犁然有契于心者。遂携入晚坞山中。衍而成之。题之曰晚坞尚志录。噫程子尝言人之为学。学处患乱贫贱。富贵荣达即不须学。夫君子之学。将以措诸天下也。而程子之言若是何也。盖人未有生而贵者。则贫贱乃其本分也。人于本分上。守得定持得牢。则出而需世。亦不过这道理。故曰国有道不变塞焉。行于有道之世者。即其未达之所守耳。况顺境易为而逆境难持。为学之道。须向难处做工夫。器局可养也。操守可坚也。志气可竖也。极辛苦中得平坦意味。至烦恼处得和易气象。则死生忧乐。如昼夜寒暑。相代乎前。而吾之心浩然而有馀裕矣。夫其所以至此。亦曰穷格以知其理。诚正以持其心。使内气足以胜外物。自养足以忘饥渴。然后始可以语此。岂一朝一夕外铄而袭取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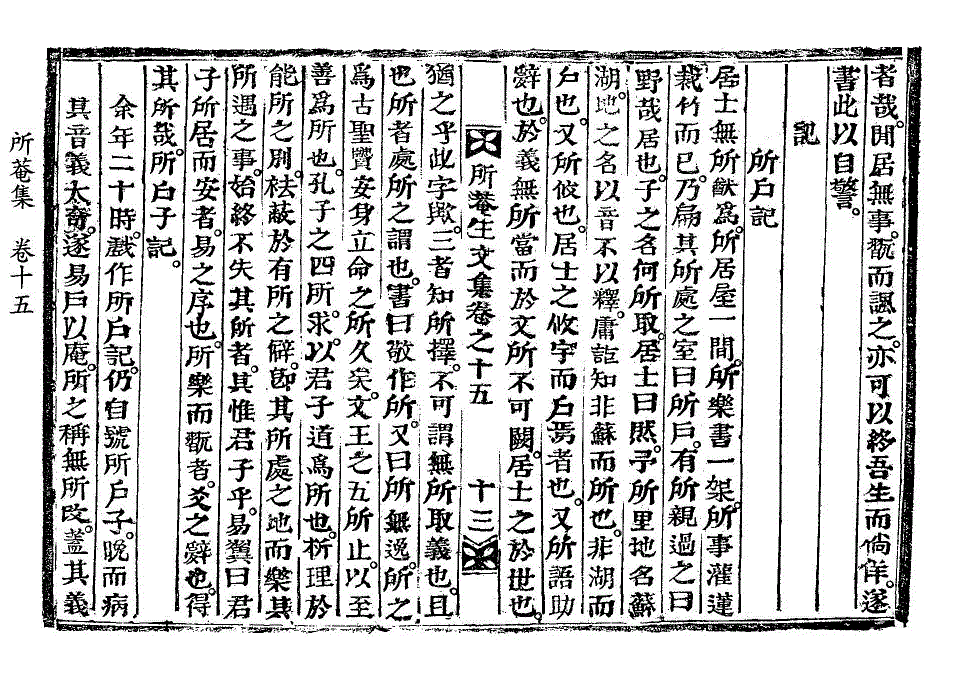 者哉。閒居无事。玩而讽之。亦可以终吾生而倘佯。遂书此以自警。
者哉。閒居无事。玩而讽之。亦可以终吾生而倘佯。遂书此以自警。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记
所户记
居士无所猷为。所居屋一间。所乐书一架。所事灌莲裁竹而已。乃扁其所处之室曰所户。有所亲过之曰野哉居也。子之名何所取。居士曰然。予所里地名苏湖。地之名以音不以释。庸讵知非苏而所也。非湖而户也。又所攸也。居士之攸宇而户焉者也。又所语助辞也。于义无所当而于文所不可阙。居士之于世也。犹之乎此字欤。三者知所择。不可谓无所取义也。且也所者处所之谓也。书曰敬作所。又曰所无逸。所之为古圣贤安身立命之所久矣。文王之五所止。以至善为所也。孔子之四所。求。以君子道为所也。析理于能所之别。祛蔽于有所之僻。即其所处之地而乐其所遇之事。始终不失其所者。其惟君子乎。易翼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得其所哉。所户子记。
余年二十时。戏作所户记。仍自号所户子。晚而病其音义太奇。遂易户以庵。所之称无所改。盖其义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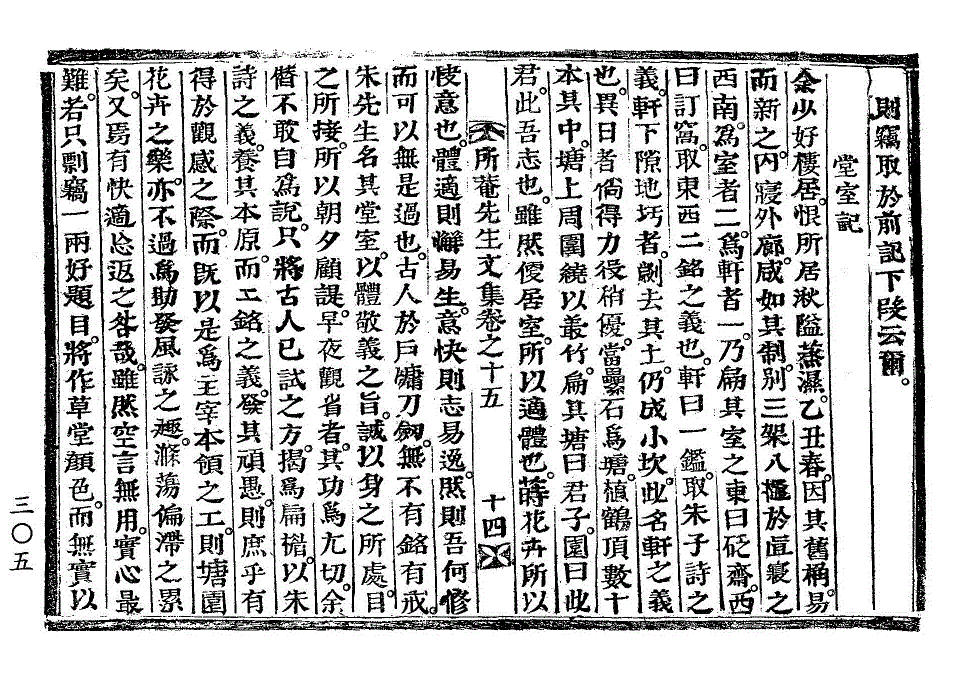 则窃取于前记下段云尔。
则窃取于前记下段云尔。堂室记
余少好楼居。恨所居湫隘蒸湿。乙丑春。因其旧桷。易而新之。内寝外廊。咸如其制。别三架八楹于直寝之西南。为室者二。为轩者一。乃扁其室之东曰砭斋。西曰订窝。取东西二铭之义也。轩曰一鉴。取朱子诗之义。轩下隙地圬者。刿去其土。仍成小坎。此名轩之义也。异日者倘得力役稍优。当累石为塘。植鹤顶数十本其中。塘上周围绕以丛竹。扁其塘曰君子。园曰此君。此吾志也。虽然便居室。所以适体也。莳花卉所以快意也。体适则懈易生。意快则志易逸。然则吾何修而可以无是过也。古人于户牖刀剑。无不有铭有戒。朱先生名其堂室。以体敬义之旨。诚以身之所处。目之所接。所以朝夕顾諟。早夜观省者。其功为尤切。余僭不敢自为说。只将古人已试之方。揭为扁楣。以朱诗之义。养其本原。而工铭之义。发其顽愚。则庶乎有得于观感之际。而既以是为主宰本领之工。则塘园花卉之乐。亦不过为助发风咏之趣。涤荡偏滞之累矣。又焉有快适忘返之咎哉。虽然空言无用。实心最难。若只剽窃一两好题目。将作草堂颜色。而无实以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6H 页
 充养之。则向所戒志逸而懈生者。岂不大可惧。而墙壁标榜。徒归于朱先生所戒铺摊门外。道我家有许多饭者。此又不可不戒也。聊记之。以足楣扁未尽之意云。乙丑中夏书。
充养之。则向所戒志逸而懈生者。岂不大可惧。而墙壁标榜。徒归于朱先生所戒铺摊门外。道我家有许多饭者。此又不可不戒也。聊记之。以足楣扁未尽之意云。乙丑中夏书。南陲晚家记
直晚修斋以南止溪之北。为吾兄弟燕寝。稍后面南小阜平夷可屋。吾先人实有意焉。乙亥冬。伯氏罢官归休。一日谋诸弟曰吾欲依山俯水。遗世务绝纷冗。以一架一炉。潜心送老如何。吾欲明窗燠室。奉我慈氏。朝夕寝处其夹。承候安否如何。吾欲大被长枕。同堂共榻。以与若辈。无斯须离也如何。吾欲大搆书舍。以与吾兄弟子孙处也。以无废先人之业。世世永赖如何。吾欲修饰旧德。以与若辈经理。以裕我尝礿如何。吾欲高楼芸香。去蠹与鼠。贮先人遗墨。仍以关键陶山之书。百世其承如何。曰惟玆六大事。实先人之所念而吾之愿也。余为汝听。佥曰诺。非兹邱奚以归。乃立三楹六架。为房者三。为轩者一。楼一库一。东一房曰顺庵。为吾老亲寝。西一房曰好窝。为吾兄弟谋。后设二架一房曰无咎斋。为后生隶业地。轩曰夕阳。楼曰百承。库曰吉蠲。合之为南陲晚家。其名义各寓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6L 页
 其所慕也。结搆既成。季弟秉远进曰大道也废而文为滋。庠舍相望。顾其实有不戾于名矣乎。吾家耄肇刱玆基。制度略具。惟玆晚玩之斋。实启关钥。修而明之。足以裕后。玆搆之设。不已赘乎。且也鲁壁苔侵。周舍葵生。本之不务。屋于何有。噫君陈之诰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将为一家之政乎。吾伯氏早荐于时。尝谷于京而绂于县。归而隐约自藏。欲修饰其素好。以为久远计。玆屋之就。其亦晚矣。王摩诘诗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噫微斯义。吾谁与归。
其所慕也。结搆既成。季弟秉远进曰大道也废而文为滋。庠舍相望。顾其实有不戾于名矣乎。吾家耄肇刱玆基。制度略具。惟玆晚玩之斋。实启关钥。修而明之。足以裕后。玆搆之设。不已赘乎。且也鲁壁苔侵。周舍葵生。本之不务。屋于何有。噫君陈之诰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其将为一家之政乎。吾伯氏早荐于时。尝谷于京而绂于县。归而隐约自藏。欲修饰其素好。以为久远计。玆屋之就。其亦晚矣。王摩诘诗曰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噫微斯义。吾谁与归。俛斋记
伯氏年就傅。在先王考侧受句读。辄仰首轩眉。气昂昂高骞。王考为书俛庵二字以畀之曰。尔可自号也。盖戏而勉又期之也。伯氏退而藏之。顾年尚少。不敢自标榜。既而从叔父寝郎公取而自扁。则又严不敢请。遂已之。日漱石翁闻之曰否。先生命也。不可以不识也。无宁易庵以斋。使其义两存可乎。伯氏曰诺。俛字有刺着头做将去之意。是吾顶针也。礼已孤不更名。重受命也。况于至戒之所寓。其敢斯须忘。朱先生诗曰佩韦遵考训。其斯之谓乎。谨集王考手字。刻之楣间。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7H 页
 永平山水可游者记
永平山水可游者记踏尽天下好山水。交尽当世好人物。读尽天下好文字。古人三愿。诚吾所寤寐想者。而文字之好。聪明日减。人物之交。形迹殊碍。独方域窄矣。足迹犹多不及。吾甚愧焉。丙子春。久直东陵。郁郁如鸟之笼而絷。不能以飞。乃以天中之日。交付僚者。飏言于众曰闻永平多奇观。谁可从者。 崇陵僚权子皓诺焉。以初七日约退院店。当日入泮中。崔孺瑞颇欲偕。以无骑不能成。临发成三律以道恨。七日雨。傍视者嘲其有天公戏。余曰无尔也。朱先生遇雨解西铭。韩愈氏为文开衡山云。今日之行。雨亦可晴亦可。遂乘雨出东小门。天渐爽。纤云遂捲。马上拈一绝云能天不能人。吾道古如玆。一雨洗尘埃。山水更逞奇。午后到退院。子皓来待已久矣。相视一笑。日已晏。不可以前。遂止宿。送子皓还 崇斋。旅灯残梦。太半是永平前路矣。八日晨子皓至。发行可十馀里。望见丰壤。大阙遗址宛然。盖 太祖晚年。经芳硕之乱。自咸兴来御于此云。午憩 光陵寺。 陵即 世祖珠丘之地。山自白云迤遭而至。雄浑杰卓。垓子周围百馀里。盖当日廷臣有以太广难之者。 上曰后日东郊之民。其将有赖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7L 页
 乎。即文王刍荛与共之意也。圣人虑远之仁若是哉。入上库。观古藏杂玩。皆 世祖在宥时所服用器物。简朴坚致。不似近日华丽轻软。亦可以想象古今文质之不侔矣。还上房。雨又作。食进而止。促发踰广岘。少憩抱川场街。乘昏宿万世桥。距京一百三十里。沿路诸闾落。皆龙州赵氏家云。九日促治行。闻白鹭洲即八景之一而前距才数弓近。直沿溪行寻。有巨石蜿蜒伏水中。余登而俯。色白水齧。有剜镵状。下数十馀步。有小岛石高可三四仞。水环其左右。跨奴背乱流至岛。岛前高后垂。白石平衍。可坐者数级。至最高处。石皆侧立。嵚𡾟攀拊。由石罅而南下。据石台俯临之。水清滢可意。老松生其顶。荫覆苍翠。樵者剪其一枝。萧索甚可怜也。东墩遇水而止。前结以岩石如帽纛。西墩石壁削立。皆相距未一弓。高下相等。与岛岩列为三岩。两崖间白沙平分而水左右流。奇秀可观。有前人刻题在石面。漫漶不可读。岛后未十武。乱石簇簇。水声中。西岸大石离立。大刻白鹭洲三字。傍书丁卯秋。观察使东罔书。岂吾岭金先生。尝按察是州耶。摩挲久之。坐水中盘石上移晷。呼笔墨大题石上曰葛西山人李慎可。子皓亦自题权子皓三字。子皓
乎。即文王刍荛与共之意也。圣人虑远之仁若是哉。入上库。观古藏杂玩。皆 世祖在宥时所服用器物。简朴坚致。不似近日华丽轻软。亦可以想象古今文质之不侔矣。还上房。雨又作。食进而止。促发踰广岘。少憩抱川场街。乘昏宿万世桥。距京一百三十里。沿路诸闾落。皆龙州赵氏家云。九日促治行。闻白鹭洲即八景之一而前距才数弓近。直沿溪行寻。有巨石蜿蜒伏水中。余登而俯。色白水齧。有剜镵状。下数十馀步。有小岛石高可三四仞。水环其左右。跨奴背乱流至岛。岛前高后垂。白石平衍。可坐者数级。至最高处。石皆侧立。嵚𡾟攀拊。由石罅而南下。据石台俯临之。水清滢可意。老松生其顶。荫覆苍翠。樵者剪其一枝。萧索甚可怜也。东墩遇水而止。前结以岩石如帽纛。西墩石壁削立。皆相距未一弓。高下相等。与岛岩列为三岩。两崖间白沙平分而水左右流。奇秀可观。有前人刻题在石面。漫漶不可读。岛后未十武。乱石簇簇。水声中。西岸大石离立。大刻白鹭洲三字。傍书丁卯秋。观察使东罔书。岂吾岭金先生。尝按察是州耶。摩挲久之。坐水中盘石上移晷。呼笔墨大题石上曰葛西山人李慎可。子皓亦自题权子皓三字。子皓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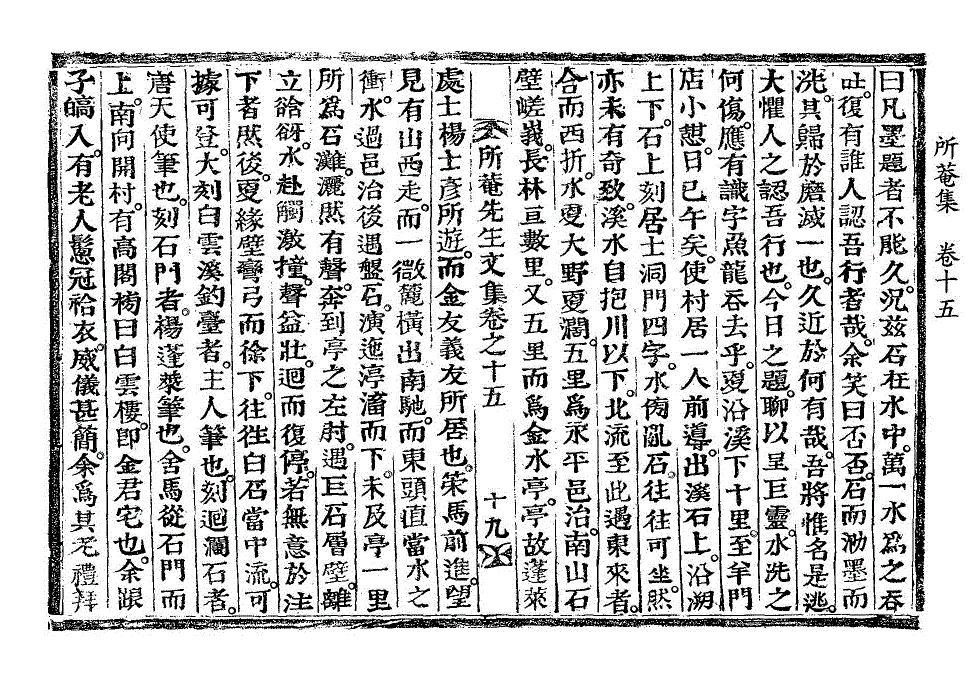 曰凡墨题者不能久。况玆石在水中。万一水为之吞吐。复有谁人认吾行者哉。余笑曰否否。石而泐墨而洗。其归于磨灭一也。久近于何有哉。吾将惟名是逃。大惧人之认吾行也。今日之题。聊以呈巨灵。水洗之何伤。应有识字鱼龙吞去乎。更沿溪下十里。至羊门店小憩。日已午矣。使村居一人前导。出溪石上。沿溯上下。石上刻居士洞门四字。水傍乱石。往往可坐。然亦未有奇致。溪水自抱川以下。北流至此遇东来者。合而西折。水更大野更阔。五里为永平邑治。南山石壁嵯峨。长林亘数里。又五里而为金水亭。亭故蓬莱处士杨士彦所游。而金友义友所居也。策马前进。望见有山西走。而一微麓横出南驰。而东头直当水之冲。水过邑治后遇盘石。演迤渟滀而下。未及亭一里所为石滩。洒然有声。奔到亭之左肘。遇巨石层壁。离立谽谺。水赴触激撞。声益壮。回而复停。若无意于注下者然后。更缘壁弯弓而徐下。往往白石当中流。可据可登。大刻白云溪钓台者。主人笔也。刻回澜石者。唐天使笔也。刻石门者。杨蓬莱笔也。舍马从石门而上。南向开村。有高阁榜曰白云楼。即金君宅也。余跟子皓入。有老人𩮰冠袷衣。威仪甚简。余为其老礼拜
曰凡墨题者不能久。况玆石在水中。万一水为之吞吐。复有谁人认吾行者哉。余笑曰否否。石而泐墨而洗。其归于磨灭一也。久近于何有哉。吾将惟名是逃。大惧人之认吾行也。今日之题。聊以呈巨灵。水洗之何伤。应有识字鱼龙吞去乎。更沿溪下十里。至羊门店小憩。日已午矣。使村居一人前导。出溪石上。沿溯上下。石上刻居士洞门四字。水傍乱石。往往可坐。然亦未有奇致。溪水自抱川以下。北流至此遇东来者。合而西折。水更大野更阔。五里为永平邑治。南山石壁嵯峨。长林亘数里。又五里而为金水亭。亭故蓬莱处士杨士彦所游。而金友义友所居也。策马前进。望见有山西走。而一微麓横出南驰。而东头直当水之冲。水过邑治后遇盘石。演迤渟滀而下。未及亭一里所为石滩。洒然有声。奔到亭之左肘。遇巨石层壁。离立谽谺。水赴触激撞。声益壮。回而复停。若无意于注下者然后。更缘壁弯弓而徐下。往往白石当中流。可据可登。大刻白云溪钓台者。主人笔也。刻回澜石者。唐天使笔也。刻石门者。杨蓬莱笔也。舍马从石门而上。南向开村。有高阁榜曰白云楼。即金君宅也。余跟子皓入。有老人𩮰冠袷衣。威仪甚简。余为其老礼拜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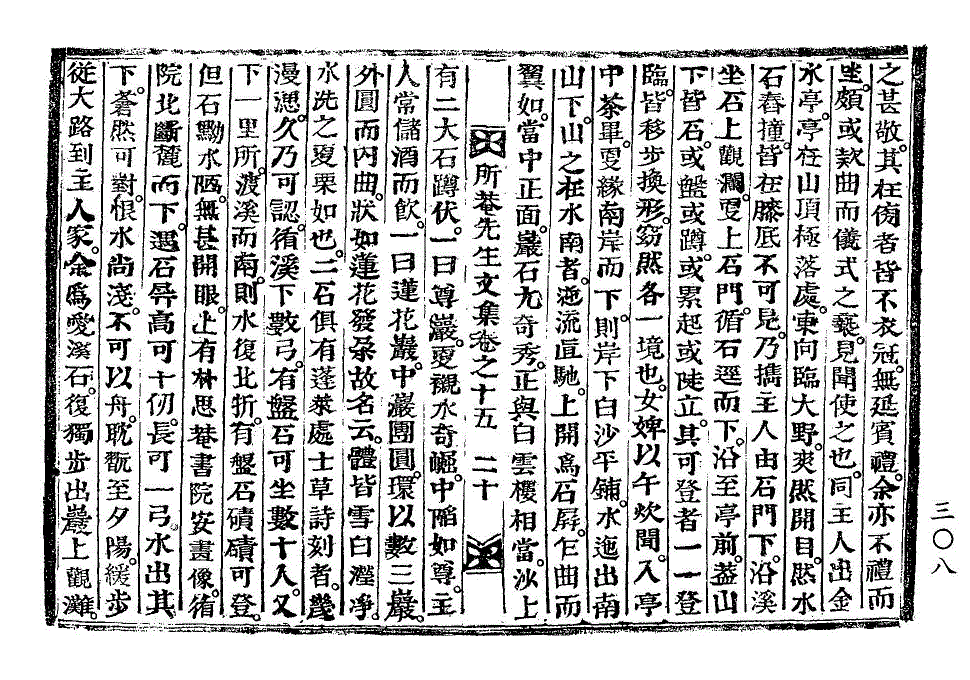 之甚敬。其在傍者皆不衣冠。无延宾礼。余亦不礼而坐。颇或款曲而仪式之亵。见闻使之也。同主人出金水亭。亭在山顶极落处。东向临大野。爽然开目。然水石舂撞。皆在膝底不可见。乃携主人由石门下。沿溪坐石上观澜。更上石门。循石径而下。沿至亭前。盖山下皆石。或盘或蹲。或累起或陡立。其可登者一一登临。皆移步换形。窈然各一境也。女婢以午炊闻。入亭中茶毕。更缘南岸而下。则岸下白沙平铺。水迤出南山下。山之在水南者。逆流直驰。上开为石屏。乍曲而翼如。当中正面。岩石尤奇秀。正与白云楼相当。沙上有二大石蹲伏。一曰尊岩。更衬水奇崛。中陷如尊。主人常储酒而饮。一曰莲花岩。中岩团圆。环以数三岩。外圆而内曲。状如莲花发朵故名云。体皆雪白滢净。水洗之更栗如也。二石俱有蓬莱处士草诗刻者。几漫漶。久乃可认。循溪下数弓。有盘石可坐数十人。又下一里所。渡溪而南。则水复北折。有盘石碛碛可登。但石黝水陋。无甚开眼。上有朴思庵书院安画像。循院北断麓而下。遇石屏高可十仞。长可一弓。水出其下。苍然可对。恨水尚浅。不可以舟。耽玩至夕阳。缓步从大路到主人家。余为爱溪石。复独步出岩上观滩。
之甚敬。其在傍者皆不衣冠。无延宾礼。余亦不礼而坐。颇或款曲而仪式之亵。见闻使之也。同主人出金水亭。亭在山顶极落处。东向临大野。爽然开目。然水石舂撞。皆在膝底不可见。乃携主人由石门下。沿溪坐石上观澜。更上石门。循石径而下。沿至亭前。盖山下皆石。或盘或蹲。或累起或陡立。其可登者一一登临。皆移步换形。窈然各一境也。女婢以午炊闻。入亭中茶毕。更缘南岸而下。则岸下白沙平铺。水迤出南山下。山之在水南者。逆流直驰。上开为石屏。乍曲而翼如。当中正面。岩石尤奇秀。正与白云楼相当。沙上有二大石蹲伏。一曰尊岩。更衬水奇崛。中陷如尊。主人常储酒而饮。一曰莲花岩。中岩团圆。环以数三岩。外圆而内曲。状如莲花发朵故名云。体皆雪白滢净。水洗之更栗如也。二石俱有蓬莱处士草诗刻者。几漫漶。久乃可认。循溪下数弓。有盘石可坐数十人。又下一里所。渡溪而南。则水复北折。有盘石碛碛可登。但石黝水陋。无甚开眼。上有朴思庵书院安画像。循院北断麓而下。遇石屏高可十仞。长可一弓。水出其下。苍然可对。恨水尚浅。不可以舟。耽玩至夕阳。缓步从大路到主人家。余为爱溪石。复独步出岩上观滩。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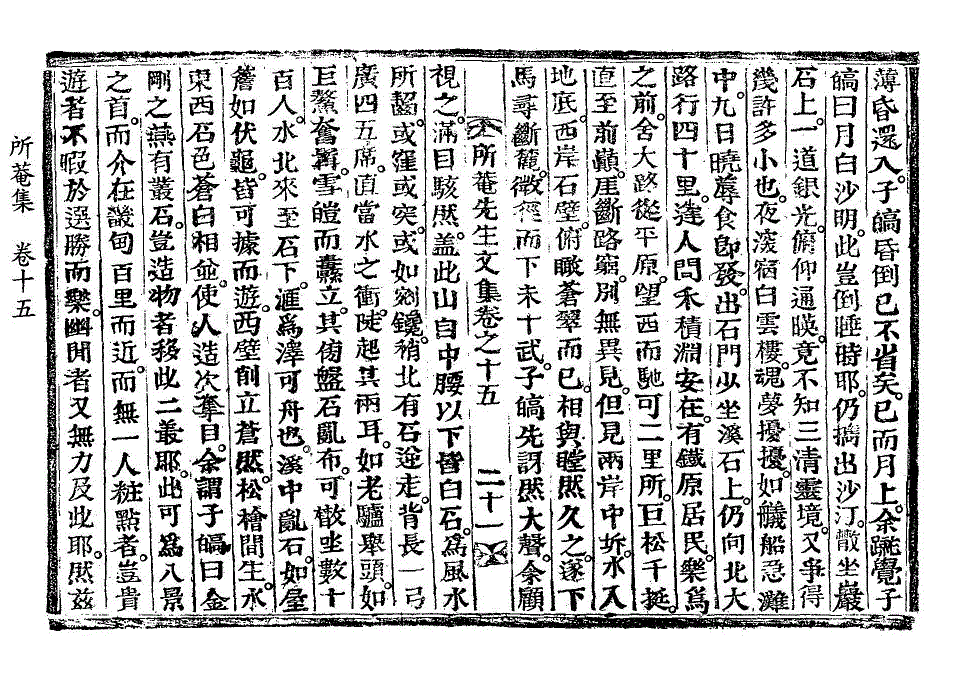 薄昏还入。子皓昏倒已不省矣。已而月上。余蹴觉子皓曰月白沙明。此岂倒睡时耶。仍携出沙汀。散坐岩石上。一道银光。俯仰通映。竟不知三清灵境。又争得几许多小也。夜深宿白云楼。魂梦扰扰。如舣船急滩中。九日晓蓐食即发。出石门少坐溪石上。仍向北大路行四十里。逢人问禾积渊安在。有铁原居民。乐为之前。舍大路从平原。望西而驰可二里所。巨松千挺。直至前巅。厓断路穷。别无异见。但见两岸中坼。水入地底。西岸石壁。俯瞰苍翠而已。相与瞠然久之。遂下马寻断麓。微径而下未十武。子皓先讶然大声。余顾视之。满目骇然。盖此山自中腰以下皆白石。为风水所齧。或洼或突。或如剜镵。稍北有石逆走。背长一弓广四五席。直当水之冲。陡起其两耳。如老驴举头。如巨鳌奋髯。雪皑而纛立。其傍盘石乱布。可散坐数十百人。水北来至石下。汇为泽可舟也。溪中乱石。如屋檐如伏龟。皆可据而游。西壁削立苍然。松桧间生。水东西石色苍白相并。使人造次夺目。余谓子皓曰金刚之燕有丛石。岂造物者移此二丛耶。此可为八景之首。而介在畿甸百里而近。而无一人妆点者。岂贵游者不暇于选胜而乐。幽閒者又无力及此耶。然玆
薄昏还入。子皓昏倒已不省矣。已而月上。余蹴觉子皓曰月白沙明。此岂倒睡时耶。仍携出沙汀。散坐岩石上。一道银光。俯仰通映。竟不知三清灵境。又争得几许多小也。夜深宿白云楼。魂梦扰扰。如舣船急滩中。九日晓蓐食即发。出石门少坐溪石上。仍向北大路行四十里。逢人问禾积渊安在。有铁原居民。乐为之前。舍大路从平原。望西而驰可二里所。巨松千挺。直至前巅。厓断路穷。别无异见。但见两岸中坼。水入地底。西岸石壁。俯瞰苍翠而已。相与瞠然久之。遂下马寻断麓。微径而下未十武。子皓先讶然大声。余顾视之。满目骇然。盖此山自中腰以下皆白石。为风水所齧。或洼或突。或如剜镵。稍北有石逆走。背长一弓广四五席。直当水之冲。陡起其两耳。如老驴举头。如巨鳌奋髯。雪皑而纛立。其傍盘石乱布。可散坐数十百人。水北来至石下。汇为泽可舟也。溪中乱石。如屋檐如伏龟。皆可据而游。西壁削立苍然。松桧间生。水东西石色苍白相并。使人造次夺目。余谓子皓曰金刚之燕有丛石。岂造物者移此二丛耶。此可为八景之首。而介在畿甸百里而近。而无一人妆点者。岂贵游者不暇于选胜而乐。幽閒者又无力及此耶。然玆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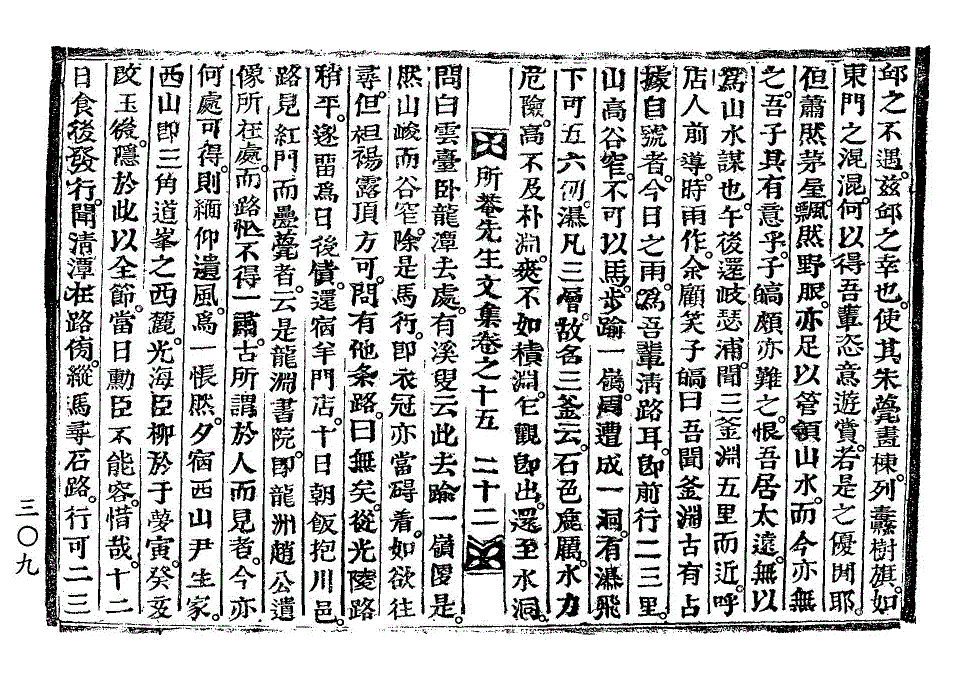 邱之不遇。玆邱之幸也。使其朱甍画栋。列纛树旗。如东门之混混。何以得吾辈恣意游赏。若是之优閒耶。但萧然茅屋。飘然野服。亦足以管领山水。而今亦无之。吾子其有意乎。子皓颇亦难之。恨吾居太远。无以为山水谋也。午后还岐瑟浦。闻三釜渊五里而近。呼店人前导。时雨作。余顾笑子皓曰吾闻釜渊古有占据自号者。今日之雨。为吾辈清路耳。即前行二三里。山高谷窄。不可以马。步踰一岭。周遭成一洞。有瀑飞下可五六仞。瀑凡三层。故名三釜云。石色粗厉。水力危险。高不及朴渊。爽不如积渊。乍观即出。还至水洞。问白云台卧龙潭去处。有溪叟云此去踰一岭便是。然山峻而谷窄。除是马行。即衣冠亦当碍着。如欲往寻。但袒裼露顶方可。问有他条路。曰无矣。从光陵路稍平。遂留为日后债。还宿羊门店。十日朝饭抱川邑。路见红门而叠甍者。云是龙渊书院。即龙洲赵公遗像所在处。而路忙不得一肃。古所谓于人而见者。今亦何处可得。则缅仰遗风。为一怅然。夕宿西山尹生家。西山即三角道峰之西麓。光海臣柳于于梦寅。癸亥改玉后。隐于此以全节。当日勋臣不能容。惜哉。十二日食后发行。闻清潭在路傍。纵马寻石路。行可二三
邱之不遇。玆邱之幸也。使其朱甍画栋。列纛树旗。如东门之混混。何以得吾辈恣意游赏。若是之优閒耶。但萧然茅屋。飘然野服。亦足以管领山水。而今亦无之。吾子其有意乎。子皓颇亦难之。恨吾居太远。无以为山水谋也。午后还岐瑟浦。闻三釜渊五里而近。呼店人前导。时雨作。余顾笑子皓曰吾闻釜渊古有占据自号者。今日之雨。为吾辈清路耳。即前行二三里。山高谷窄。不可以马。步踰一岭。周遭成一洞。有瀑飞下可五六仞。瀑凡三层。故名三釜云。石色粗厉。水力危险。高不及朴渊。爽不如积渊。乍观即出。还至水洞。问白云台卧龙潭去处。有溪叟云此去踰一岭便是。然山峻而谷窄。除是马行。即衣冠亦当碍着。如欲往寻。但袒裼露顶方可。问有他条路。曰无矣。从光陵路稍平。遂留为日后债。还宿羊门店。十日朝饭抱川邑。路见红门而叠甍者。云是龙渊书院。即龙洲赵公遗像所在处。而路忙不得一肃。古所谓于人而见者。今亦何处可得。则缅仰遗风。为一怅然。夕宿西山尹生家。西山即三角道峰之西麓。光海臣柳于于梦寅。癸亥改玉后。隐于此以全节。当日勋臣不能容。惜哉。十二日食后发行。闻清潭在路傍。纵马寻石路。行可二三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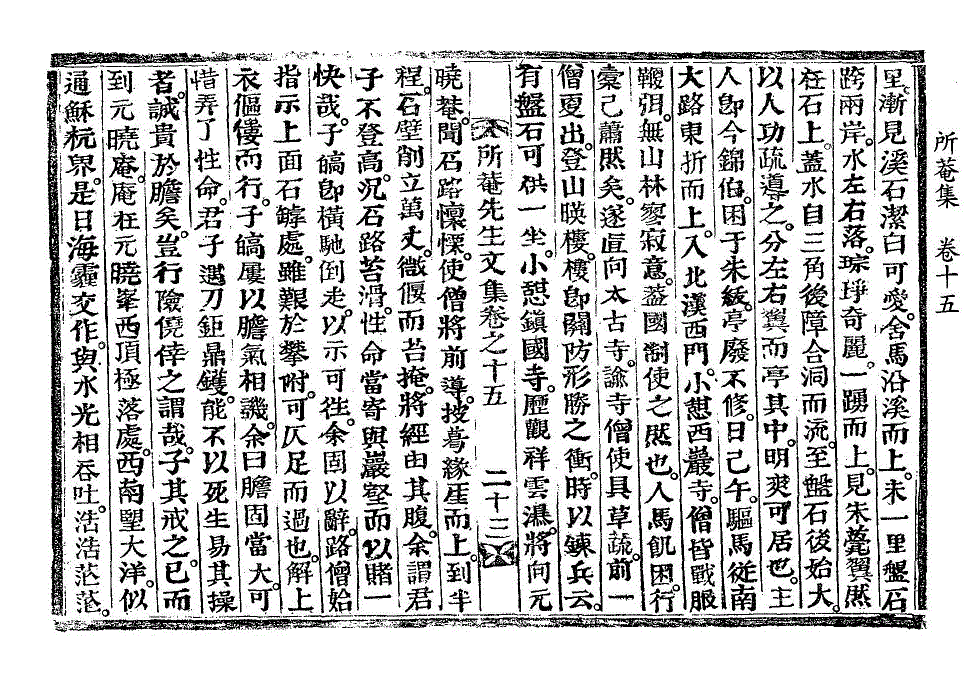 里。渐见溪石洁白可爱。舍马沿溪而上。未一里盘石跨两岸。水左右落。琮琤奇丽。一踊而上。见朱甍翼然在石上。盖水自三角后障合洞而流。至盘石后始大。以人功疏导之。分左右翼而亭其中。明爽可居也。主人即今锦伯。困于朱绂。亭废不修。日已午。驱马从南大路东折而上。入北汉西门。小憩西岩寺。僧皆战服鞭弭。无山林寥寂意。盖国制使之然也。人马饥困。行橐已萧然矣。遂直向太古寺。谕寺僧使具草蔬。前一僧更出。登山映楼。楼即关防形胜之冲。时以鍊兵云。有盘石可供一坐。小憩镇国寺。历观祥云瀑。将向元晓庵。闻石路懔慄。使僧将前导。披葛缘厓而上。到半程。石壁削立万丈。微偃而苔掩。将经由其腹。余谓君子不登高。况石路苔滑。性命当寄与岩壑而以赌一快哉。子皓即横驰倒走。以示可往。余固以辞。路僧始指示上面石罅处。虽艰于攀附。可仄足而过也。解上衣伛偻而行。子皓屡以胆气相讥。余曰胆固当大。可惜弄了性命。君子遇刀钜鼎镬。能不以死生易其操者。诚贵于胆矣。岂行险侥倖之谓哉。子其戒之。已而到元晓庵。庵在元晓峰西顶极落处。西南望大洋。似通稣杭界。是日海霾交作。与水光相吞吐。浩浩茫茫。
里。渐见溪石洁白可爱。舍马沿溪而上。未一里盘石跨两岸。水左右落。琮琤奇丽。一踊而上。见朱甍翼然在石上。盖水自三角后障合洞而流。至盘石后始大。以人功疏导之。分左右翼而亭其中。明爽可居也。主人即今锦伯。困于朱绂。亭废不修。日已午。驱马从南大路东折而上。入北汉西门。小憩西岩寺。僧皆战服鞭弭。无山林寥寂意。盖国制使之然也。人马饥困。行橐已萧然矣。遂直向太古寺。谕寺僧使具草蔬。前一僧更出。登山映楼。楼即关防形胜之冲。时以鍊兵云。有盘石可供一坐。小憩镇国寺。历观祥云瀑。将向元晓庵。闻石路懔慄。使僧将前导。披葛缘厓而上。到半程。石壁削立万丈。微偃而苔掩。将经由其腹。余谓君子不登高。况石路苔滑。性命当寄与岩壑而以赌一快哉。子皓即横驰倒走。以示可往。余固以辞。路僧始指示上面石罅处。虽艰于攀附。可仄足而过也。解上衣伛偻而行。子皓屡以胆气相讥。余曰胆固当大。可惜弄了性命。君子遇刀钜鼎镬。能不以死生易其操者。诚贵于胆矣。岂行险侥倖之谓哉。子其戒之。已而到元晓庵。庵在元晓峰西顶极落处。西南望大洋。似通稣杭界。是日海霾交作。与水光相吞吐。浩浩茫茫。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0L 页
 遂不分天海矣。海中岛屿隐隐如黑子。膝下诸山蚓走蛇蟠。若掌上数纹。诚壮观也。庵与义相窟南北相持。昔日高僧元晓,义相。分山居此故名云。白云台在元晓东。又其东为露积峰。通为三角寺。僧云两峰皆石路危险。往往陡断。蚁附而上。非判命不可到。遂还自西城。从西岩左肩而上。城壕形胜。大略在眼中矣。城盖以备国家缓急之用。仓库蓄积甚盛。今皆枵然空矣。射夫炮僧。乱发前后山若儿戏然。山外环而内凹。可为天堑。然城内崎窄。无鍊兵之地。还宿太古寺。翌朝前马蹑屩。历行宫观普光寺。出文殊门西。缘石径行数弓。有石窟在山中央。安五百罗汉。有一僧供粥饭。小憩道场。南临景福城形胜。盖山自白头而来。至金刚逞一大奇。仍抽其一麓。左挟汉江。右挟临津。千里而驰。挺为道峰。奇秀灵特。遂颓而下结而上。为三角。雄伟诡异。孕气藏精。皆所以尽造化用意之巧。而南起为文殊峰。则山皆南向而俯列如钜齿。奔若湫倒。精神之所辏泊。气力之所驱使。似狂似惊而后结一大咽。耸为负儿岳。则㥘气尽而光华浮。奔腾之意隐而雍容之味胜矣。我国家亿万无疆之休。殆所谓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乎。因拖迤而下。则道径颇广而地势陡陷。
遂不分天海矣。海中岛屿隐隐如黑子。膝下诸山蚓走蛇蟠。若掌上数纹。诚壮观也。庵与义相窟南北相持。昔日高僧元晓,义相。分山居此故名云。白云台在元晓东。又其东为露积峰。通为三角寺。僧云两峰皆石路危险。往往陡断。蚁附而上。非判命不可到。遂还自西城。从西岩左肩而上。城壕形胜。大略在眼中矣。城盖以备国家缓急之用。仓库蓄积甚盛。今皆枵然空矣。射夫炮僧。乱发前后山若儿戏然。山外环而内凹。可为天堑。然城内崎窄。无鍊兵之地。还宿太古寺。翌朝前马蹑屩。历行宫观普光寺。出文殊门西。缘石径行数弓。有石窟在山中央。安五百罗汉。有一僧供粥饭。小憩道场。南临景福城形胜。盖山自白头而来。至金刚逞一大奇。仍抽其一麓。左挟汉江。右挟临津。千里而驰。挺为道峰。奇秀灵特。遂颓而下结而上。为三角。雄伟诡异。孕气藏精。皆所以尽造化用意之巧。而南起为文殊峰。则山皆南向而俯列如钜齿。奔若湫倒。精神之所辏泊。气力之所驱使。似狂似惊而后结一大咽。耸为负儿岳。则㥘气尽而光华浮。奔腾之意隐而雍容之味胜矣。我国家亿万无疆之休。殆所谓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者乎。因拖迤而下。则道径颇广而地势陡陷。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1H 页
 往往无住脚处。所谓矩步而绳趍者。于此更着不得矣。行可十馀里。遇一谷水潺湲可沿。白石往往盘溪上。浣纱女高下晒衣。问知为造纸署。又一曲而为平仓。居民栉比。又循麓而下。有临溪练楮者。即纸工业纸处。小憩绕麓而瑰。见白石益龃龉。水由石罅下。琮琮可听。未数弓盘石上。画阁飘然。榜曰洗剑亭。前临白石晴川。后有石陡起为台。刻鍊戎坛三字。至柳亭下骑马。出捍北门。即北汉外城门。北汉之观止矣。门外有石泉庵。庵傍摩厓刻石佛。岩前削壁上。有满城妓挟乐而唱。红绿管笙。隐映林木间。盖有药水生其上云。出弘济院。踰鞍岘入圯桥子皓家。数间茅屋。萧然在城市间。相与打话。或乱抽架上书。已而白饭香蔬。萧洒可口。对案毕即叙别。入西小门。驰到泮中。盖七日来复矣。由历二百馀里。领略湖海壮观。穷洛阳之形胜。觇名园之盛衰。可谓追小鲁之辙。跨禹穴之策。自觉烟霞拍拍生两腋矣。崔孺瑞亟来相问。又就朱张两先生祝融韵。为和三首以侈之。且要余作行程记。以资其卧游。余于山水游历。故不喜为诗若记。独玆一行。既有吾子所嘱。且以谷口子曾有同游之约。而今千里而遥。而吾为之先着矣。不可使不知则
往往无住脚处。所谓矩步而绳趍者。于此更着不得矣。行可十馀里。遇一谷水潺湲可沿。白石往往盘溪上。浣纱女高下晒衣。问知为造纸署。又一曲而为平仓。居民栉比。又循麓而下。有临溪练楮者。即纸工业纸处。小憩绕麓而瑰。见白石益龃龉。水由石罅下。琮琮可听。未数弓盘石上。画阁飘然。榜曰洗剑亭。前临白石晴川。后有石陡起为台。刻鍊戎坛三字。至柳亭下骑马。出捍北门。即北汉外城门。北汉之观止矣。门外有石泉庵。庵傍摩厓刻石佛。岩前削壁上。有满城妓挟乐而唱。红绿管笙。隐映林木间。盖有药水生其上云。出弘济院。踰鞍岘入圯桥子皓家。数间茅屋。萧然在城市间。相与打话。或乱抽架上书。已而白饭香蔬。萧洒可口。对案毕即叙别。入西小门。驰到泮中。盖七日来复矣。由历二百馀里。领略湖海壮观。穷洛阳之形胜。觇名园之盛衰。可谓追小鲁之辙。跨禹穴之策。自觉烟霞拍拍生两腋矣。崔孺瑞亟来相问。又就朱张两先生祝融韵。为和三首以侈之。且要余作行程记。以资其卧游。余于山水游历。故不喜为诗若记。独玆一行。既有吾子所嘱。且以谷口子曾有同游之约。而今千里而遥。而吾为之先着矣。不可使不知则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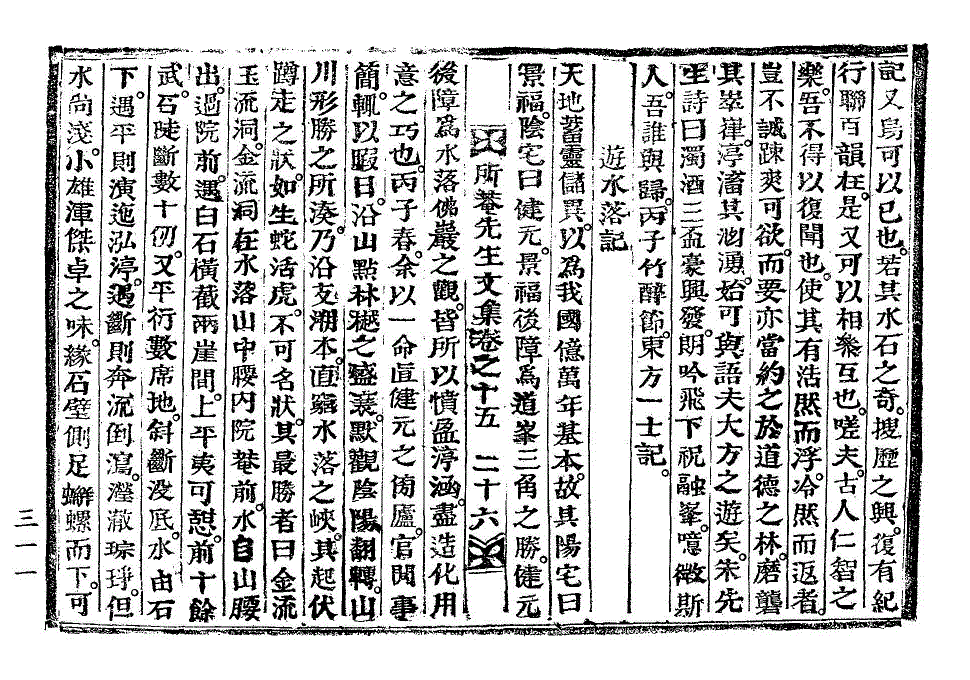 记又乌可以已也。若其水石之奇。搜历之兴。复有纪行联百韵在。是又可以相参互也。嗟夫。古人仁智之乐。吾不得以复闻也。使其有浩然而浮。冷然而返者。岂不诚疏爽可欲。而要亦当约之于道德之林。磨砻其崒嵂。渟滀其汹涌。始可与语夫大方之游矣。朱先生诗曰浊酒三杯豪兴发。朗吟飞下祝融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丙子竹醉节。东方一士记。
记又乌可以已也。若其水石之奇。搜历之兴。复有纪行联百韵在。是又可以相参互也。嗟夫。古人仁智之乐。吾不得以复闻也。使其有浩然而浮。冷然而返者。岂不诚疏爽可欲。而要亦当约之于道德之林。磨砻其崒嵂。渟滀其汹涌。始可与语夫大方之游矣。朱先生诗曰浊酒三杯豪兴发。朗吟飞下祝融峰。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丙子竹醉节。东方一士记。游水落记
天地蓄灵储异。以为我国亿万年基本。故其阳宅曰景福。阴宅曰健元。景福后障为道峰三角之胜。健元后障为水落佛岩之观。皆所以愤盈渟涵。尽造化用意之巧也。丙子春。余以一命直健元之傍庐。官閒事简。辄以暇日。沿山点林樾之盛衰。默观阴阳翻转。山川形胜之所凑。乃沿支溯本。直穷水落之峡。其起伏蹲走之状。如生蛇活虎。不可名状。其最胜者曰金流玉流洞。金流洞在水落山中腰内院庵前。水自山腰出。过院前。遇白石横截两崖间。上平夷可憩。前十馀武。石陡断数十仞。又平衍数席地。斜断没底。水由石下。遇平则演迤泓渟。遇断则奔流倒泻。滢澈琮琤。但水尚浅。小雄浑杰卓之味。缘石壁侧足蟹螺而下。可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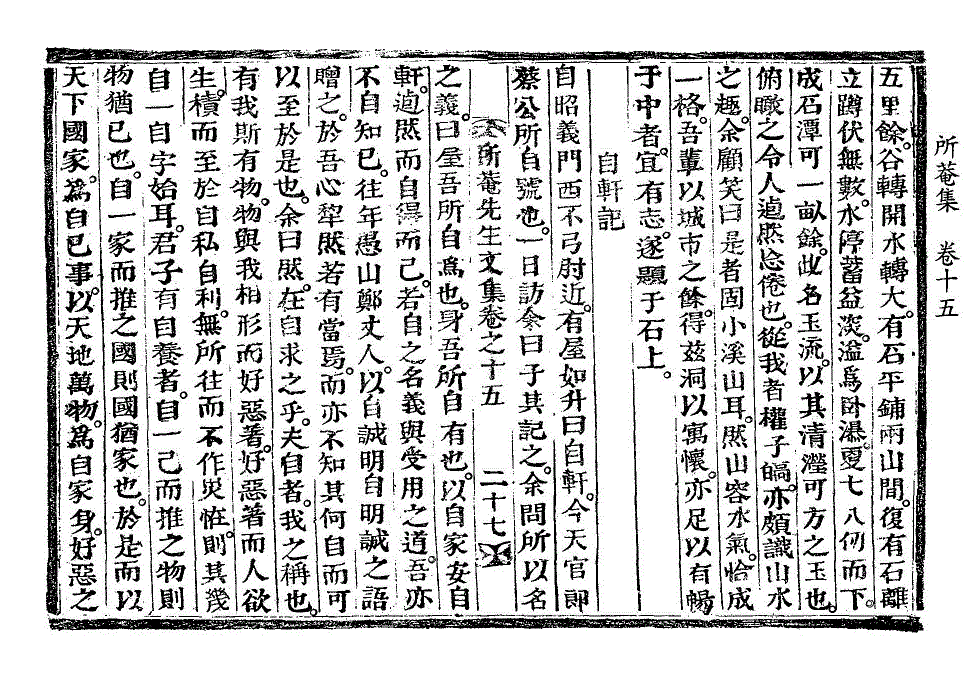 五里馀。谷转开水转大。有石平铺两山间。复有石离立蹲伏无数。水停蓄益深。溢为卧瀑。更七八仞而下。成石潭可一亩馀。此名玉流。以其清滢可方之玉也。俯瞰之令人逌然忘倦也。从我者权子皓。亦颇识山水之趣。余顾笑曰是者固小溪山耳。然山容水气。恰成一格。吾辈以城市之馀。得玆洞以寓怀。亦足以有畅于中者。宜有志。遂题于石上。
五里馀。谷转开水转大。有石平铺两山间。复有石离立蹲伏无数。水停蓄益深。溢为卧瀑。更七八仞而下。成石潭可一亩馀。此名玉流。以其清滢可方之玉也。俯瞰之令人逌然忘倦也。从我者权子皓。亦颇识山水之趣。余顾笑曰是者固小溪山耳。然山容水气。恰成一格。吾辈以城市之馀。得玆洞以寓怀。亦足以有畅于中者。宜有志。遂题于石上。自轩记
自昭义门西不弓肘近。有屋如升曰自轩。今天官郎蔡公所自号也。一日访余曰子其记之。余问所以名之义。曰屋吾所自为也。身吾所自有也。以自家安自轩。逌然而自得而已。若自之名义与受用之道。吾亦不自知已。往年愚山郑丈人。以自诚明自明诚之语赠之。于吾心犁然若有当焉。而亦不知其何自而可以至于是也。余曰然。在自求之乎。夫自者。我之称也。有我斯有物。物与我相形而好恶著。好恶著而人欲生。积而至于自私自利。无所往而不作灾怪。则其几自一自字始耳。君子有自养者。自一己而推之物则物犹己也。自一家而推之国则国犹家也。于是而以天下国家。为自己事。以天地万物。为自家身。好恶之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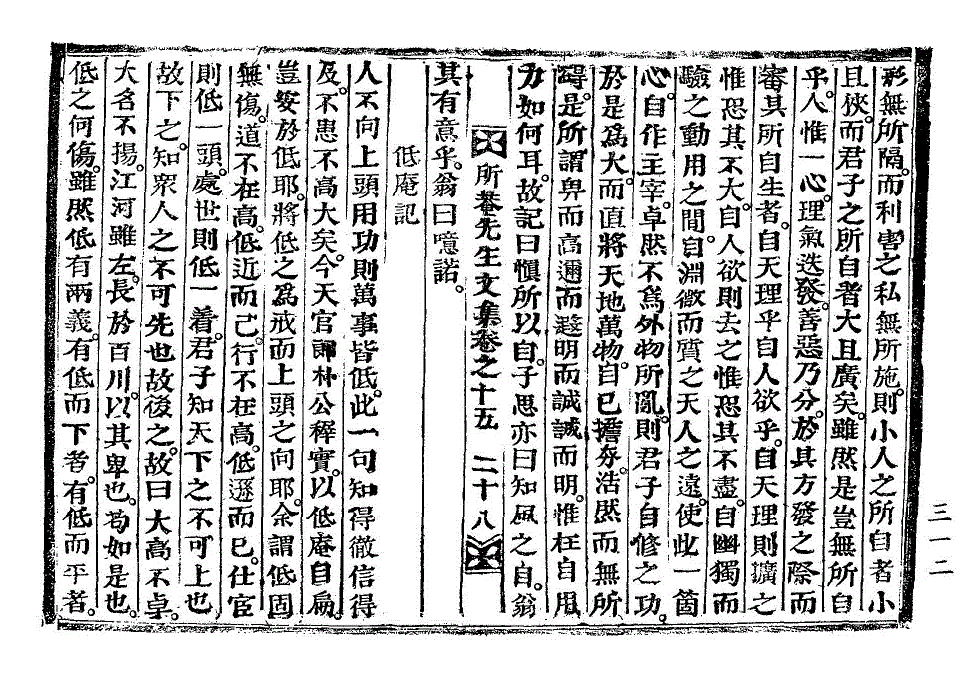 形无所隔。而利害之私无所施。则小人之所自者小且狭。而君子之所自者大且广矣。虽然是岂无所自乎。人惟一心。理气迭发。善恶乃分。于其方发之际而审其所自生者。自天理乎自人欲乎。自天理则扩之惟恐其不大。自人欲则去之惟恐其不尽。自幽独而验之动用之间。自渊微而质之天人之远。使此一个心。自作主宰。卓然不为外物所乱。则君子自修之功。于是为大。而直将天地万物。自己担夯。浩然而无所碍。是所谓卑而高迩而遐明而诚诚而明。惟在自用力如何耳。故记曰慎所以自。子思亦曰知风之自。翁其有意乎。翁曰噫诺。
形无所隔。而利害之私无所施。则小人之所自者小且狭。而君子之所自者大且广矣。虽然是岂无所自乎。人惟一心。理气迭发。善恶乃分。于其方发之际而审其所自生者。自天理乎自人欲乎。自天理则扩之惟恐其不大。自人欲则去之惟恐其不尽。自幽独而验之动用之间。自渊微而质之天人之远。使此一个心。自作主宰。卓然不为外物所乱。则君子自修之功。于是为大。而直将天地万物。自己担夯。浩然而无所碍。是所谓卑而高迩而遐明而诚诚而明。惟在自用力如何耳。故记曰慎所以自。子思亦曰知风之自。翁其有意乎。翁曰噫诺。低庵记
人不向上头用功则万事皆低。此一句知得彻信得及。不患不高大矣。今天官郎朴公稚实。以低庵自扁。岂安于低耶。将低之为戒而上头之向耶。余谓低固无伤。道不在高。低近而已。行不在高。低逊而已。仕宦则低一头。处世则低一着。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故曰大高不卓。大名不扬。江河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苟如是也。低之何伤。虽然低有两义。有低而下者。有低而平者。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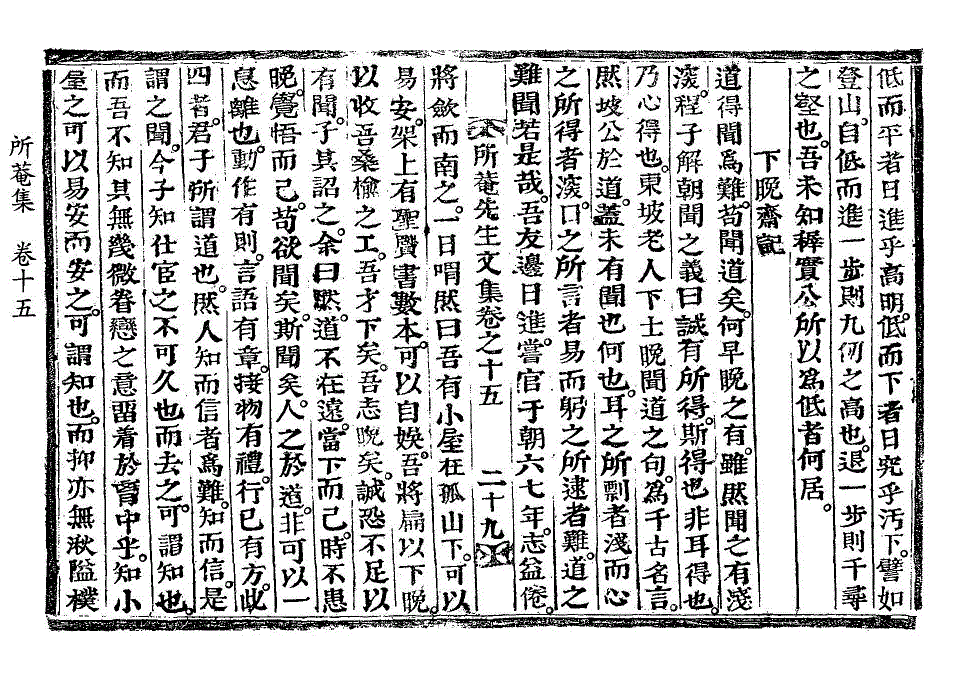 低而平者日进乎高明。低而下者日究乎污下。譬如登山。自低而进一步则九仞之高也。退一步则千寻之壑也。吾未知稚实公所以为低者何居。
低而平者日进乎高明。低而下者日究乎污下。譬如登山。自低而进一步则九仞之高也。退一步则千寻之壑也。吾未知稚实公所以为低者何居。下晚斋记
道得闻为难。苟闻道矣。何早晚之有。虽然闻之有浅深。程子解朝闻之义曰诚有所得。斯得也非耳得也。乃心得也。东坡老人下士晚闻道之句。为千古名言。然坡公于道。盖未有闻也何也。耳之所剽者浅而心之所得者深。口之所言者易而躬之所逮者难。道之难闻若是哉。吾友边日进。尝官于朝六七年。志益倦。将敛而南之。一日喟然曰吾有小屋在孤山下。可以易安。架上有圣贤书数本。可以自娱。吾将扁以下晚。以收吾桑榆之工。吾才下矣。吾志晚矣。诚恐不足以有闻。子其诏之。余曰然。道不在远。当下而已。时不患晚。觉悟而已。苟欲闻矣。斯闻矣。人之于道。非可以一息离也。动作有则。言语有章。接物有礼。行己有方。此四者。君子所谓道也。然人知而信者为难。知而信。是谓之闻。今子知仕宦之不可久也而去之。可谓知也。而吾不知其无几微眷恋之意留着于胸中乎。知小屋之可以易安而安之。可谓知也。而抑亦无湫隘朴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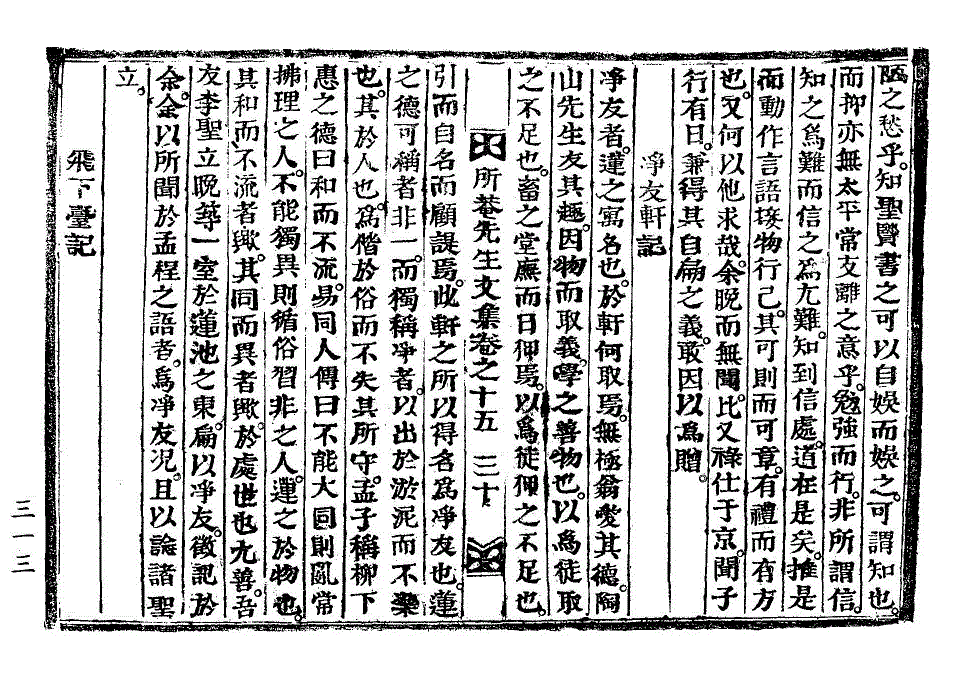 陋之愁乎。知圣贤书之可以自娱而娱之。可谓知也。而抑亦无太平常支离之意乎。勉强而行。非所谓信。知之为难而信之为尤难。知到信处。道在是矣。推是而动作言语接物行己。其可则而可章。有礼而有方也。又何以他求哉。余晚而无闻。比又禄仕于京。闻子行有日。兼得其自扁之义。敢因以为赠。
陋之愁乎。知圣贤书之可以自娱而娱之。可谓知也。而抑亦无太平常支离之意乎。勉强而行。非所谓信。知之为难而信之为尤难。知到信处。道在是矣。推是而动作言语接物行己。其可则而可章。有礼而有方也。又何以他求哉。余晚而无闻。比又禄仕于京。闻子行有日。兼得其自扁之义。敢因以为赠。净友轩记
净友者。莲之寓名也。于轩何取焉。无极翁爱其德。陶山先生友其趣。因物而取义。学之善物也。以为徒取之不足也。畜之堂庑而日狎焉。以为徒狎之不足也。引而自名而顾諟焉。此轩之所以得名为净友也。莲之德可称者非一。而独称净者。以出于淤泥而不染也。其于人也。为偕于俗而不失其所守。孟子称柳下惠之德曰和而不流。易同人传曰不能大同则乱常拂理之人。不能独异则循俗习非之人。莲之于物也。其和而不流者欤。其同而异者欤。于处世也尤善。吾友李圣立晚筑一室于莲池之东。扁以净友。徵记于余。余以所闻于孟程之语者。为净友况。且以谂诸圣立。
飞下台记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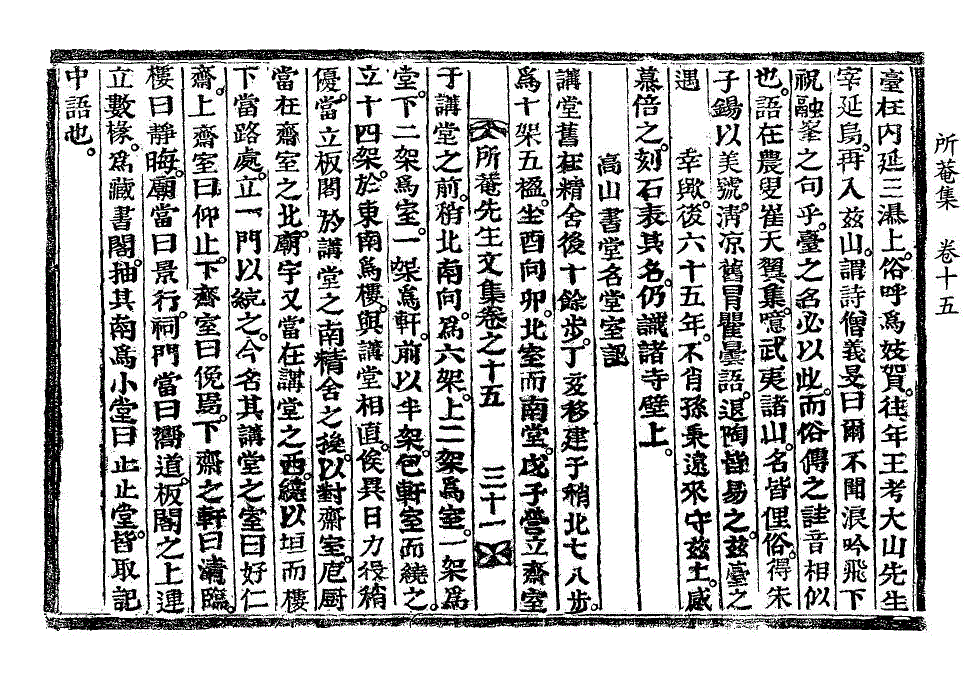 台在内延三瀑上。俗呼为妓贺。往年王考大山先生宰延乌。再入玆山。谓诗僧义旻曰尔不闻浪吟飞下祝融峰之句乎。台之名必以此。而俗传之诖音相似也。语在农叟崔天翼集。噫武夷诸山。名皆俚俗。得朱子锡以美号。清凉旧冒瞿昙语。退陶皆易之。玆台之遇▣▣(不亦)幸欤。后六十五年。不肖孙秉远来守玆土。感慕倍之。刻石表其名。仍识诸寺壁上。
台在内延三瀑上。俗呼为妓贺。往年王考大山先生宰延乌。再入玆山。谓诗僧义旻曰尔不闻浪吟飞下祝融峰之句乎。台之名必以此。而俗传之诖音相似也。语在农叟崔天翼集。噫武夷诸山。名皆俚俗。得朱子锡以美号。清凉旧冒瞿昙语。退陶皆易之。玆台之遇▣▣(不亦)幸欤。后六十五年。不肖孙秉远来守玆土。感慕倍之。刻石表其名。仍识诸寺壁上。高山书堂名堂室记
讲堂旧在精舍后十馀步。丁亥移建于稍北七八步。为十架五楹。坐酉向卯。北室而南堂。戊子营立斋室于讲堂之前。稍北南向。为六架。上二架为室。一架为堂。下二架为室。一架为轩。前以半架。包轩室而绕之。立十四架。于东南为楼。与讲堂相直。俟异日力役稍优。当立板阁于讲堂之南精舍之后。以对斋室。庖厨当在斋室之北。庙宇又当在讲堂之西。绕以垣而楼下当路处。立一门以统之。今名其讲堂之室曰好仁斋。上斋室曰仰止。下斋室曰俛焉。下斋之轩曰清临。楼曰静晦。庙当曰景行。祠门当曰向道。板阁之上连立数椽。为藏书阁。抽其南为小堂曰止止堂。皆取记中语也。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4L 页
 晚坞书堂记事
晚坞书堂记事晚坞书堂。在大夕山北麓开口处。中峰遇野而止。前为小墩。龙虎稍引而前。仅藏一屋。两端石壁嵯峨。前临大坪。禾塍高下相连平如盘。水自鼎岭发源。十折过乌峰。抱山北东迤走。山如蛇行。水如弓弯。至龟村前。与白虎相遇。若敛衽然而水隐于此。直堂之前面有澄潭。其上苍壁往往戴土。其上有石方正而脩洁者。有平面而圆广者。其外龟潭之山。如趍揖相向然。王考大山先生尝有诛茅之意。今集中所载行视后山五律二首即此地。而痛慕录曰所居山北有小区。岩谷谽谺。境界静僻。每有结庐之意。轩曰后凋。斋东曰夕惕。西曰岁寒。合而扁之曰晚坞书堂。盖取义于山名之大夕也。号名已成而屋子未就者。即记实也。今按此诗成于戊寅。则经始实在高山卜筑之前。而其后己亥庚子间。又欲诛茅。因事而止。盖先生既得高山后。亦未尝忘此地也。前有水田数区。亦当时所营置。为凿池计。而中因亭不举而田亦转而为他人有矣。余在清河时。以本直还其田。因有肯搆之意。顾力转绵。意况转瘁。不能以及。今年春。诸同人锐意经记。遂不能禁。为房十尺者三架。以其一自占。以其二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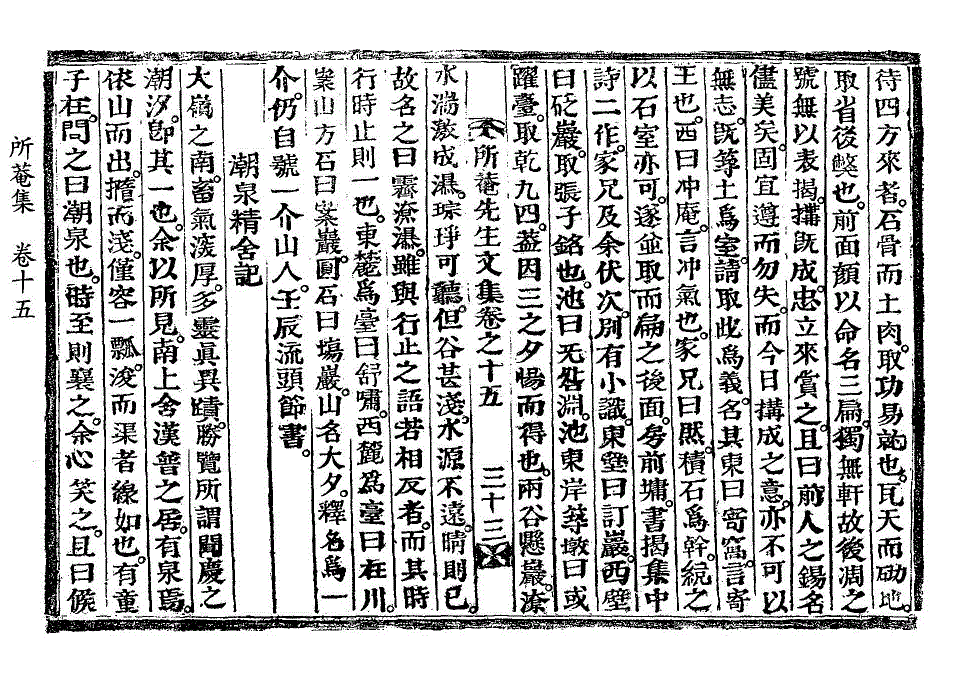 待四方来者。石骨而土肉。取功易就也。瓦天而砌地。取省后弊也。前面颜以命名三扁。独无轩故后凋之号无以表揭。搆既成。忠立来赏之。且曰前人之锡名尽美矣。固宜遵而勿失。而今日搆成之意。亦不可以无志。既筑土为室。请取此为义。名其东曰寄窝。言寄王也。西曰冲庵。言冲气也。家兄曰然。积石为干。统之以石室亦可。遂并取而扁之后面。房前墉。书揭集中诗二作。家兄及余伏次。别有小识。东壁曰订岩。西壁曰砭岩。取张子铭也。池曰无咎渊。池东岸筑墩曰或跃台。取乾九四。盖因三之夕惕而得也。两谷悬岩。潦水湍激成瀑。琮琤可听。但谷甚浅。水源不远。晴则已。故名之曰霁潦瀑。虽与行止之语若相反者。而其时行时止则一也。东麓为台曰舒啸。西麓为台曰在川。案山方石曰案岩。圆石曰场岩。山名大夕。释名为一介。仍自号一介山人。壬辰流头节书。
待四方来者。石骨而土肉。取功易就也。瓦天而砌地。取省后弊也。前面颜以命名三扁。独无轩故后凋之号无以表揭。搆既成。忠立来赏之。且曰前人之锡名尽美矣。固宜遵而勿失。而今日搆成之意。亦不可以无志。既筑土为室。请取此为义。名其东曰寄窝。言寄王也。西曰冲庵。言冲气也。家兄曰然。积石为干。统之以石室亦可。遂并取而扁之后面。房前墉。书揭集中诗二作。家兄及余伏次。别有小识。东壁曰订岩。西壁曰砭岩。取张子铭也。池曰无咎渊。池东岸筑墩曰或跃台。取乾九四。盖因三之夕惕而得也。两谷悬岩。潦水湍激成瀑。琮琤可听。但谷甚浅。水源不远。晴则已。故名之曰霁潦瀑。虽与行止之语若相反者。而其时行时止则一也。东麓为台曰舒啸。西麓为台曰在川。案山方石曰案岩。圆石曰场岩。山名大夕。释名为一介。仍自号一介山人。壬辰流头节书。潮泉精舍记
大岭之南。畜气深厚。多灵真异迹。胜览所谓闻庆之潮汐。即其一也。余以所见。南上舍汉普之居。有泉焉。依山而出。撱而浅。仅容一瓢。浚而渠者线如也。有童子在。问之曰潮泉也。时至则襄之。余心笑之。且曰候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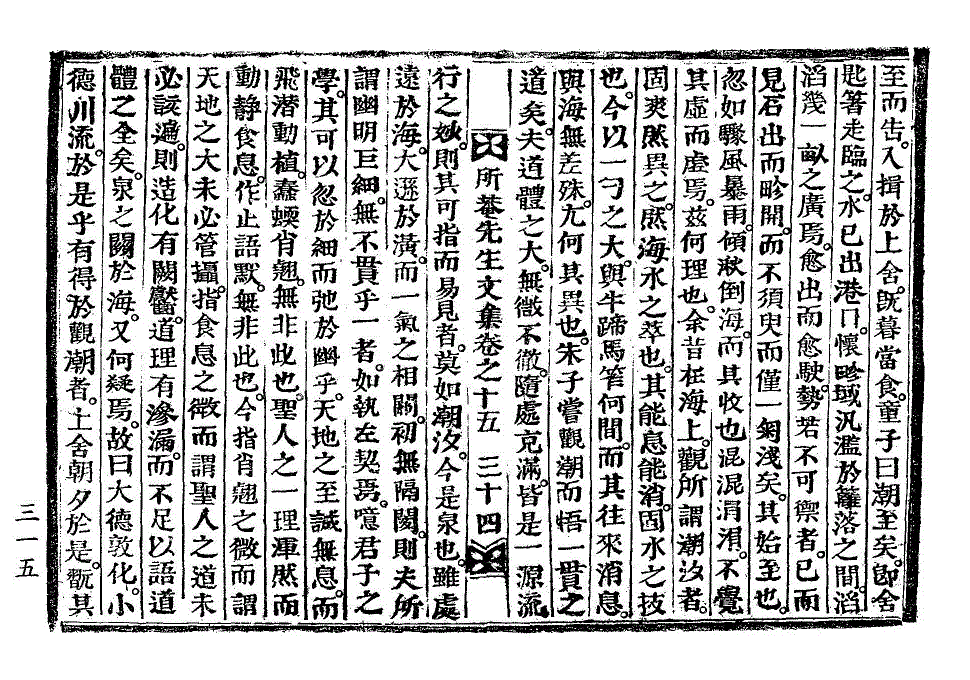 至而告。入揖于上舍。既暮当食。童子曰潮至矣。即舍匙箸走临之。水已出港口。怀畛域汎滥于篱落之间。滔滔几一亩之广焉。愈出而愈驶。势若不可御者。已而见石出而畛开。而不须臾而仅一匊浅矣。其始至也。忽如骤风㬥雨。倾湫倒海。而其收也混混涓涓。不觉其虚而虚焉。玆何理也。余昔在海上。观所谓潮汐者。固爽然异之。然海水之萃也。其能息能消。固水之技也。今以一勺之大。与牛蹄马笮何间。而其往来消息。与海无差殊。尤何其异也。朱子尝观潮而悟一贯之道矣。夫道体之大。无微不彻。随处充满。皆是一源流行之妙。则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潮汐。今是泉也。虽处远于海。大逊于潢。而一气之相关。初无隔阂。则夫所谓幽明巨细。无不贯乎一者。如执左契焉。噫君子之学。其可以忽于细而弛于幽乎。天地之至诚无息。而飞潜动植。蠢蠕肖翘。无非此也。圣人之一理浑然而动静食息。作止语默。无非此也。今指肖翘之微而谓天地之大未必管摄。指食息之微而谓圣人之道未必该遍。则造化有阙齾。道理有渗漏。而不足以语道体之全矣。泉之关于海。又何疑焉。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于是乎有得于观潮者。上舍朝夕于是。玩其
至而告。入揖于上舍。既暮当食。童子曰潮至矣。即舍匙箸走临之。水已出港口。怀畛域汎滥于篱落之间。滔滔几一亩之广焉。愈出而愈驶。势若不可御者。已而见石出而畛开。而不须臾而仅一匊浅矣。其始至也。忽如骤风㬥雨。倾湫倒海。而其收也混混涓涓。不觉其虚而虚焉。玆何理也。余昔在海上。观所谓潮汐者。固爽然异之。然海水之萃也。其能息能消。固水之技也。今以一勺之大。与牛蹄马笮何间。而其往来消息。与海无差殊。尤何其异也。朱子尝观潮而悟一贯之道矣。夫道体之大。无微不彻。随处充满。皆是一源流行之妙。则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潮汐。今是泉也。虽处远于海。大逊于潢。而一气之相关。初无隔阂。则夫所谓幽明巨细。无不贯乎一者。如执左契焉。噫君子之学。其可以忽于细而弛于幽乎。天地之至诚无息。而飞潜动植。蠢蠕肖翘。无非此也。圣人之一理浑然而动静食息。作止语默。无非此也。今指肖翘之微而谓天地之大未必管摄。指食息之微而谓圣人之道未必该遍。则造化有阙齾。道理有渗漏。而不足以语道体之全矣。泉之关于海。又何疑焉。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于是乎有得于观潮者。上舍朝夕于是。玩其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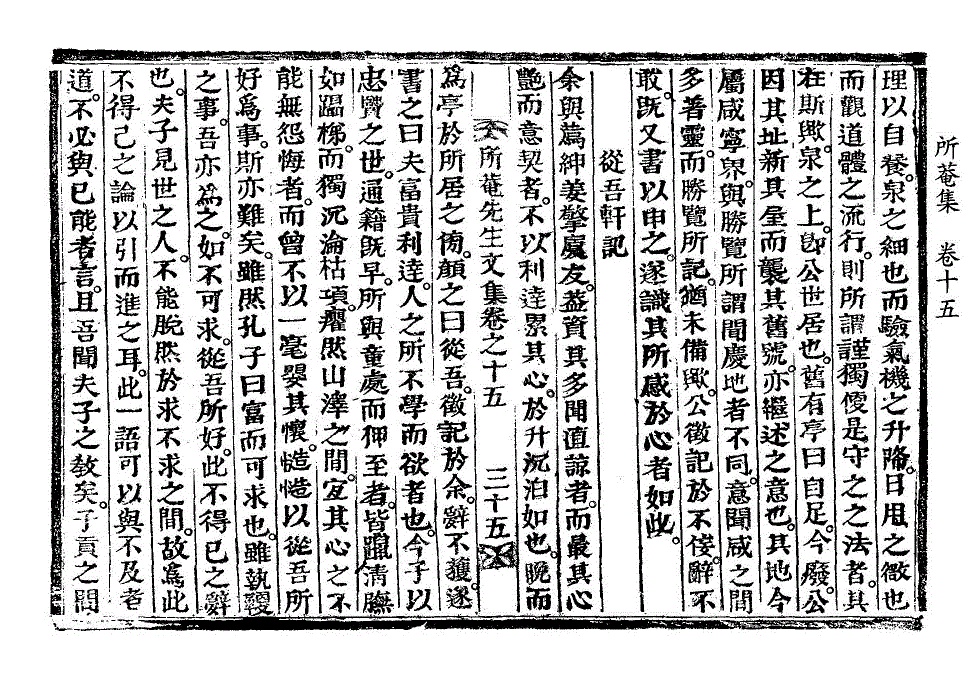 理以自养。泉之细也而验气机之升降。日用之微也而观道体之流行。则所谓谨独便是守之之法者。其在斯欤。泉之上。即公世居也。旧有亭曰自足。今废。公因其址新其屋而袭其旧号。亦继述之意也。其地今属咸宁界。与胜览所谓闻庆地者不同。意闻咸之间多著灵。而胜览所记。犹未备欤。公徵记于不佞。辞不敢。既又书以申之。遂识其所感于心者如此。
理以自养。泉之细也而验气机之升降。日用之微也而观道体之流行。则所谓谨独便是守之之法者。其在斯欤。泉之上。即公世居也。旧有亭曰自足。今废。公因其址新其屋而袭其旧号。亦继述之意也。其地今属咸宁界。与胜览所谓闻庆地者不同。意闻咸之间多著灵。而胜览所记。犹未备欤。公徵记于不佞。辞不敢。既又书以申之。遂识其所感于心者如此。从吾轩记
余与荐绅姜擎厦友。盖资其多闻直谅者。而最其心艳而意契者。不以利达累其心。于升沉泊如也。晚而为亭于所居之傍。颜之曰从吾。徵记于余。辞不获。遂书之曰夫富贵利达。人之所不学而欲者也。今子以忠贤之世。通籍既早。所与童处而狎至者。皆躐清膴如蹑梯。而独沉沦枯项。癯然山泽之间。宜其心之不能无怨悔者。而曾不以一毫婴其怀。慥慥以从吾所好为事。斯亦难矣。虽然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鞕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此不得已之辞也。夫子见世之人。不能脱然于求不求之间。故为此不得已之论以引而进之耳。此一语可以与不及者道。不必与已能者言。且吾闻夫子之教矣。子贡之问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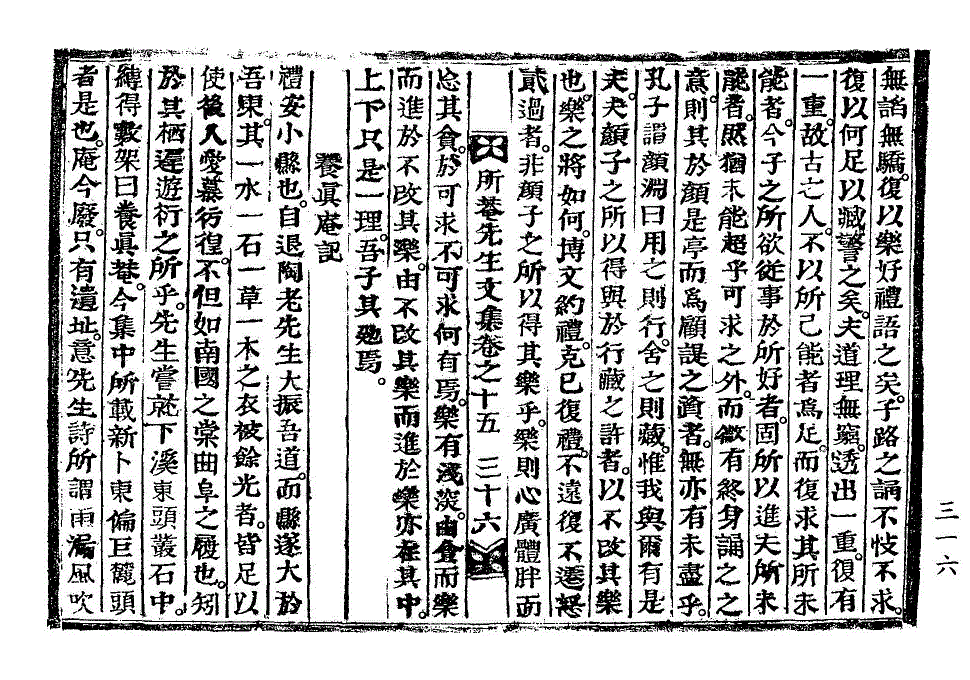 无谄无骄。复以乐好礼语之矣。子路之诵不忮不求。复以何足以臧警之矣。夫道理无穷。透出一重。复有一重。故古之人。不以所已能者为足。而复求其所未能者。今子之所欲从事于所好者。固所以进夫所未能者。然犹未能超乎可求之外。而微有终身诵之之意。则其于颜是亭而为顾諟之资者。无亦有未尽乎。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夫颜子之所以得与于行藏之许者。以不改其乐也。乐之将如何。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不远复不迁怒贰过者。非颜子之所以得其乐乎。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于可求不可求何有焉。乐有浅深。由贫而乐而进于不改其乐。由不改其乐而进于乐亦在其中。上下只是一理。吾子其勉焉。
无谄无骄。复以乐好礼语之矣。子路之诵不忮不求。复以何足以臧警之矣。夫道理无穷。透出一重。复有一重。故古之人。不以所已能者为足。而复求其所未能者。今子之所欲从事于所好者。固所以进夫所未能者。然犹未能超乎可求之外。而微有终身诵之之意。则其于颜是亭而为顾諟之资者。无亦有未尽乎。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夫颜子之所以得与于行藏之许者。以不改其乐也。乐之将如何。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不远复不迁怒贰过者。非颜子之所以得其乐乎。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于可求不可求何有焉。乐有浅深。由贫而乐而进于不改其乐。由不改其乐而进于乐亦在其中。上下只是一理。吾子其勉焉。养真庵记
礼安小县也。自退陶老先生大振吾道。而县遂大于吾东。其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衣被馀光者。皆足以使后人爱慕彷徨。不但如南国之棠曲阜之履也。矧于其栖迟游衍之所乎。先生尝就下溪东头丛石中。缚得数架曰养真庵。今集中所载新卜东偏巨麓头者是也。庵今废。只有遗址。意先生诗所谓雨漏风吹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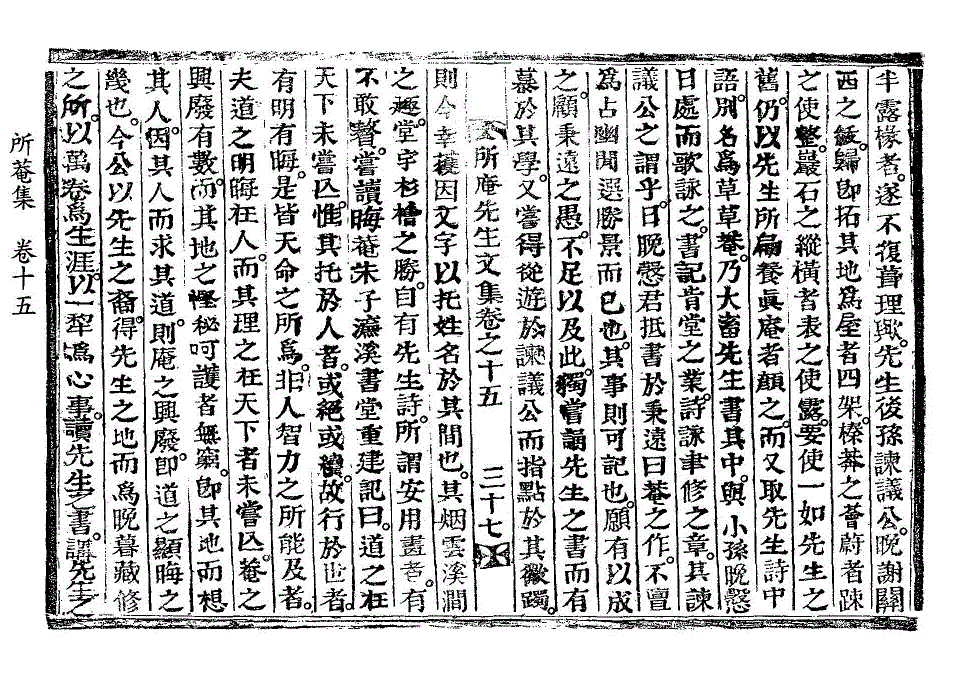 半露椽者。遂不复葺理欤。先生后孙谏议公。晚谢关西之绂。归即拓其地为屋者四架。榛莽之荟蔚者疏之使整。岩石之纵横者表之使露。要使一如先生之旧。仍以先生所扁养真庵者颜之。而又取先生诗中语。别名为草草庵。乃大畜先生书其中。与小孙晚悫日处而歌咏之。书记肯堂之业。诗咏聿修之章。其谏议公之谓乎。日晚悫君抵书于秉远曰庵之作。不亶为占幽閒选胜景而已也。其事则可记也。愿有以成之。顾秉远之愚。不足以及此。独尝诵先生之书而有慕于其学。又尝得从游于谏议公而指点于其微躅。则今幸获因文字以托姓名于其间也。其烟云溪涧之趣。堂宇杉桧之胜。自有先生诗。所谓安用画者。有不敢赘。尝读晦庵朱子濂溪书堂重建记曰。道之在天下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者。夫道之明晦在人。而其理之在天下者未尝亡。庵之兴废有数。而其地之悭秘呵护者无穷。即其地而想其人。因其人而求其道。则庵之兴废。即道之显晦之几也。今公以先生之裔。得先生之地而为晚暮藏修之所。以万卷为生涯。以一犁为心事。读先生之书。讲先生之
半露椽者。遂不复葺理欤。先生后孙谏议公。晚谢关西之绂。归即拓其地为屋者四架。榛莽之荟蔚者疏之使整。岩石之纵横者表之使露。要使一如先生之旧。仍以先生所扁养真庵者颜之。而又取先生诗中语。别名为草草庵。乃大畜先生书其中。与小孙晚悫日处而歌咏之。书记肯堂之业。诗咏聿修之章。其谏议公之谓乎。日晚悫君抵书于秉远曰庵之作。不亶为占幽閒选胜景而已也。其事则可记也。愿有以成之。顾秉远之愚。不足以及此。独尝诵先生之书而有慕于其学。又尝得从游于谏议公而指点于其微躅。则今幸获因文字以托姓名于其间也。其烟云溪涧之趣。堂宇杉桧之胜。自有先生诗。所谓安用画者。有不敢赘。尝读晦庵朱子濂溪书堂重建记曰。道之在天下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者。夫道之明晦在人。而其理之在天下者未尝亡。庵之兴废有数。而其地之悭秘呵护者无穷。即其地而想其人。因其人而求其道。则庵之兴废。即道之显晦之几也。今公以先生之裔。得先生之地而为晚暮藏修之所。以万卷为生涯。以一犁为心事。读先生之书。讲先生之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7L 页
 学。益从事于养真之工。则其于求先生之道。亦将由此其进也。是则道之晦而明。固天命之所为。而学之绝而复续。顾不在于人欤。不然而徒剔蔚搜奇。费力开宇。而于所谓真乐无涯者。不得其方。则岂公搆堂之本意哉。谏议公乐善长厚。老而不倦。晚悫君年富而志远者。其必将有以大讲先生之道而成公之志者。则庵之重新。其亦光前启后之一会也。明道先生颜乐亭诗卒章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于乎正学。其何可忘。余于是庵亦云。
学。益从事于养真之工。则其于求先生之道。亦将由此其进也。是则道之晦而明。固天命之所为。而学之绝而复续。顾不在于人欤。不然而徒剔蔚搜奇。费力开宇。而于所谓真乐无涯者。不得其方。则岂公搆堂之本意哉。谏议公乐善长厚。老而不倦。晚悫君年富而志远者。其必将有以大讲先生之道而成公之志者。则庵之重新。其亦光前启后之一会也。明道先生颜乐亭诗卒章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于乎正学。其何可忘。余于是庵亦云。光风亭重建记
敬堂张先生得陶山心学之传于鹤峰金先生。以启锦阳之学。岭南学者翕然宗之。凡先生平日杖屦游衍之地。无所不爱赏指点。以寓高山景行之思云。先生尝就春坡居第之傍。为台曰霁月。为亭曰光风。先生没后十六年。因亭而社。又十五年。移社于镜光而亭遂废。今其遗址在焉。先生后孙世奎。与一方人士。谋所以新之。既刻石表其台。又因其旧础而亭焉。使后之登斯堂者。恍然若亲侍燕閒而薰袭其光霁之容。其有功于感发兴起之助者。为不少矣。于乎。先生之必以风月二者。表揭为台与亭之号者何也。濂溪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8H 页
 夫子得千圣不传之秘。揭太极之图。发主静之旨。以指示大原。而先生所著一元消长图。实本于周子阳变阴合之妙。名堂顾諟之义。又有得于敬静合一之旨。则盖先生之学。深有契于周先生之道。而其想象彷佛于有道气像者。益亲切的当。非一时偶然标榜之比也。昔朱子尝作光风霁月亭于濂溪旧墟。使有志于濂翁之学者。即其地而想其人。因其名而得其气像。而先生主静无欲之学。风月无边之容。愀然如复见焉。则今日吾党之为是役。其亦出于讲先生之学。慕先生之风。而为吾道复振之一大机会也。亭既成。俾秉远记其事。顾藐然末学。何敢窥测于先生之道则猥有记述。诚知其僭且妄矣。然秉远固先生之自出。则其于相玆事也。亦乌可以不文辞。程先生颜乐亭诗卒章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于乎正学。其何可忘。余于是亭亦云。
夫子得千圣不传之秘。揭太极之图。发主静之旨。以指示大原。而先生所著一元消长图。实本于周子阳变阴合之妙。名堂顾諟之义。又有得于敬静合一之旨。则盖先生之学。深有契于周先生之道。而其想象彷佛于有道气像者。益亲切的当。非一时偶然标榜之比也。昔朱子尝作光风霁月亭于濂溪旧墟。使有志于濂翁之学者。即其地而想其人。因其名而得其气像。而先生主静无欲之学。风月无边之容。愀然如复见焉。则今日吾党之为是役。其亦出于讲先生之学。慕先生之风。而为吾道复振之一大机会也。亭既成。俾秉远记其事。顾藐然末学。何敢窥测于先生之道则猥有记述。诚知其僭且妄矣。然秉远固先生之自出。则其于相玆事也。亦乌可以不文辞。程先生颜乐亭诗卒章曰井不忍废。地不忍荒。于乎正学。其何可忘。余于是亭亦云。石滩亭记
石之为物。光逊于玉。不能为圭璋琬琰弘璧苍珩之珍焉。肥劣于土。不能为耕耘树艺埏填陶冶之利焉。柔下于木。不能为栋梁榱桷器用爨燧之资民生焉。则物之无用者也。然名山胜界登临游赏之所。有石
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8L 页
 则奇。无石则凡。幽人韵士栖迟藏点之地。有石则名。无石则索然无况。是盖藏用于无用之地者也。然石不能自奇。遇水而奇。水之与石遇也。为演漾喷泻洑洄沫瀑。惟石之随焉。为琮琤激触荡汹汪洋。惟石之鸣焉。石无水。顽然粗面而已。水无石。淼然潺流而已。余尝思之。石至刚也。水至柔也。刚柔相摩而后。乃能逞其技也。石至静也。水至动也。动静相涵而后。乃能遂其用也。意者造物之相宣而体用之相须也。府北周村之口。有石横两山而平之。如铺毡籍茅。不见片土焉。有水循石而下。如鸣筝撞镛。流霞走珠。日夜不暂休。直北累石为台。吾友李益文亭其上。亭据岸而高。凡石之洼突罅缝。水之缘泻停洄。无不入于轩窗中。距村落才步武而窈然别界也。余登而俯。石不大水不深。由溪而上无兹石。由石而下亦无玆石。而猝然相遇于峰回路转之间。水滢而石益白。石侧而水益驶。琮琮金石之声。竟夜而魂梦冷然也。益文属余曰先人之尝有意也。而适成于吾。固不胜孤露之感。而近偶发箧而得先人所写风树亭三大字。盖先人已有追先之思。则亭实三世之志也。将易以风树之名。子其为我记之。余谓古人跬步而不敢忘孝。故于
则奇。无石则凡。幽人韵士栖迟藏点之地。有石则名。无石则索然无况。是盖藏用于无用之地者也。然石不能自奇。遇水而奇。水之与石遇也。为演漾喷泻洑洄沫瀑。惟石之随焉。为琮琤激触荡汹汪洋。惟石之鸣焉。石无水。顽然粗面而已。水无石。淼然潺流而已。余尝思之。石至刚也。水至柔也。刚柔相摩而后。乃能逞其技也。石至静也。水至动也。动静相涵而后。乃能遂其用也。意者造物之相宣而体用之相须也。府北周村之口。有石横两山而平之。如铺毡籍茅。不见片土焉。有水循石而下。如鸣筝撞镛。流霞走珠。日夜不暂休。直北累石为台。吾友李益文亭其上。亭据岸而高。凡石之洼突罅缝。水之缘泻停洄。无不入于轩窗中。距村落才步武而窈然别界也。余登而俯。石不大水不深。由溪而上无兹石。由石而下亦无玆石。而猝然相遇于峰回路转之间。水滢而石益白。石侧而水益驶。琮琮金石之声。竟夜而魂梦冷然也。益文属余曰先人之尝有意也。而适成于吾。固不胜孤露之感。而近偶发箧而得先人所写风树亭三大字。盖先人已有追先之思。则亭实三世之志也。将易以风树之名。子其为我记之。余谓古人跬步而不敢忘孝。故于所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第 319H 页
 隐约盘旋之地。往往因地而寓感。如建安之考亭。桧渊之望云庵是也。是盖推亲亲之仁。以为游息观居之具。而张子所谓出王游衍。无一事之非仁也。今子之名亭。石滩言其胜也。风树言其志也。俱不可以偏废。而后之登斯亭者。山水之胜在溪石上。堂搆之业在扁楣间。亦无用记为也。抑公之意既笃于追先。以是而贻诸昆。以世其孝。将见亭之胜。当与石滩永其传。是则可记也。遂乐为之书。
隐约盘旋之地。往往因地而寓感。如建安之考亭。桧渊之望云庵是也。是盖推亲亲之仁。以为游息观居之具。而张子所谓出王游衍。无一事之非仁也。今子之名亭。石滩言其胜也。风树言其志也。俱不可以偏废。而后之登斯亭者。山水之胜在溪石上。堂搆之业在扁楣间。亦无用记为也。抑公之意既笃于追先。以是而贻诸昆。以世其孝。将见亭之胜。当与石滩永其传。是则可记也。遂乐为之书。十奇轩记
广于德城西南子城上。箘覆之。绳床铺之。四翾以机。今知县所户子所创也。搆既成无所名。客曰古人有为清河县民咏十奇。名于斯固当。主人曰何敢望。且也为治在平易。曷奇之以乎。顾县有十奇。动石三瀑布三大海一日出一月出一。主人以山野畸士。暂出而管之。亦一奇。合之为十。颜斯轩足矣。书之以为县中一奇事。知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