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x 页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杂著
杂著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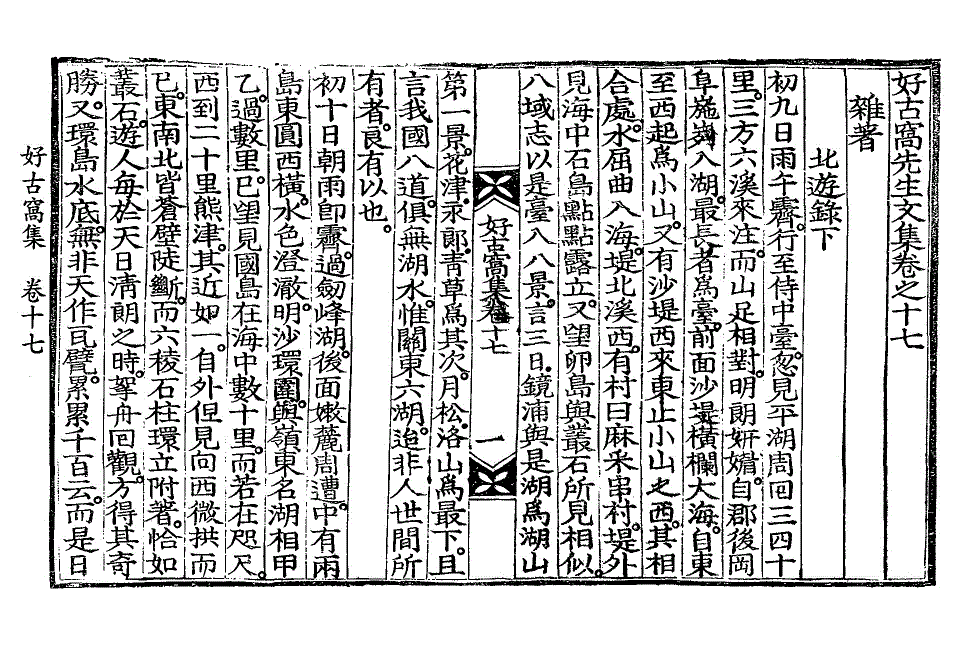 北游录[下]
北游录[下]初九日雨午霁。行至侍中台。忽见平湖周回三四十里。三方六溪来注。而山足相对。明朗妍媚。自郡后冈阜崺峛入湖。最长者为台。前面沙堤横栏大海。自东至西起为小山。又有沙堤西来东止小山之西。其相合处。水屈曲入海。堤北溪西。有村曰麻采串村。堤外见海中石岛点点露立。又望卵岛与丛石所见相似。八域志以是台入八景。言三日,镜浦与是湖为湖山第一景。花津,永郎,青草为其次。月松,洛山为最下。且言我国八道。俱无湖水。惟关东六湖。迨非人世间所有者。良有以也。
初十日朝雨即霁。过剑峰湖。后面嫩麓周遭。中有两岛东圆西横。水色澄澈。明沙环围。与岭东名湖相甲乙。过数里。已望见国岛在海中数十里。而若在咫尺。西到二十里熊津。其近如一。自外但见向西微拱而已。东南北皆苍壁陡断。而六棱石柱环立附著。恰如丛石。游人每于天日清朗之时。挐舟回观。方得其奇胜。又环岛水底。无非天作瓦甓。累累千百云。而是日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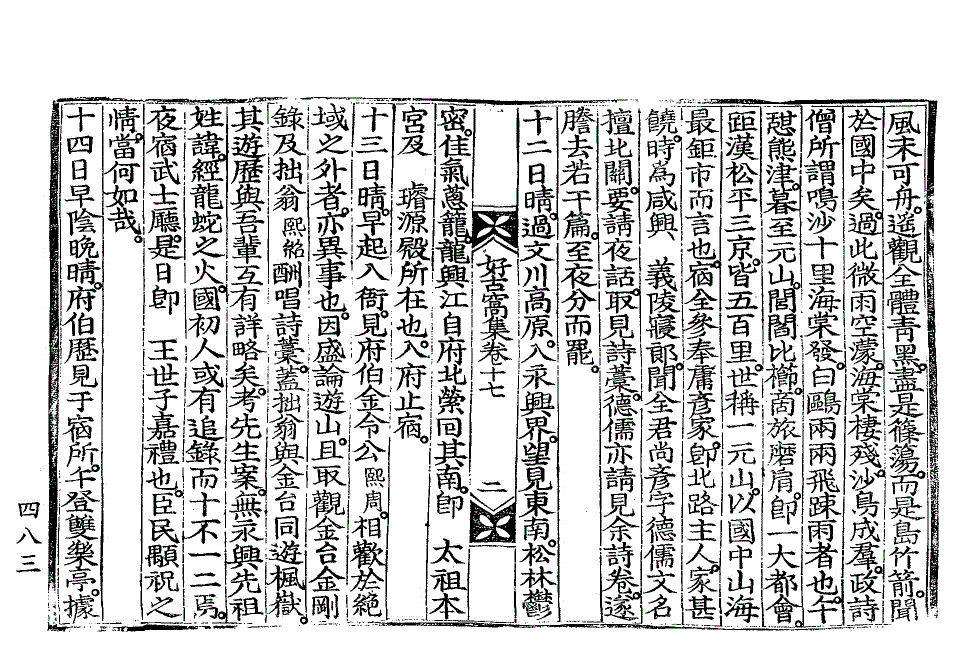 风未可舟。遥观全体青黑。尽是筱簜。而是岛竹箭。闻于国中矣。过此微雨空濛。海棠栖残。沙鸟成群。政诗僧所谓鸣沙十里海棠发。白鸥两两飞疏雨者也。午憩熊津。暮至元山。闾阎比栉。商旅磨肩。即一大都会。距汉松平三京。皆五百里。世称一元山。以国中山海最钜市而言也。宿全参奉庸彦家。即北路主人。家甚饶。时为咸兴 义陵寝郎。闻全君尚彦字德儒文名擅北关。要请夜话。取见诗藁。德儒亦请见余诗卷。遂誊去若干篇。至夜分而罢。
风未可舟。遥观全体青黑。尽是筱簜。而是岛竹箭。闻于国中矣。过此微雨空濛。海棠栖残。沙鸟成群。政诗僧所谓鸣沙十里海棠发。白鸥两两飞疏雨者也。午憩熊津。暮至元山。闾阎比栉。商旅磨肩。即一大都会。距汉松平三京。皆五百里。世称一元山。以国中山海最钜市而言也。宿全参奉庸彦家。即北路主人。家甚饶。时为咸兴 义陵寝郎。闻全君尚彦字德儒文名擅北关。要请夜话。取见诗藁。德儒亦请见余诗卷。遂誊去若干篇。至夜分而罢。十二日晴。过文川高原。入永兴界。望见东南。松林郁密。佳气葱笼。龙兴江自府北萦回其南。即 太祖本宫及 璿源殿所在也。入府止宿。
十三日晴。早起入衙。见府伯金令公(熙周)。相欢于绝域之外者。亦异事也。因盛论游山。且取观金台金刚录及拙翁(熙绍)酬唱诗藁。盖拙翁与金台同游枫岳。其游历与吾辈互有详略矣。考先生案。无永兴先祖姓讳。经龙蛇之火。国初人或有追录而十不一二焉。夜宿武士厅。是日即 王世子嘉礼也。臣民颙祝之情。当何如哉。
十四日早阴晚晴。府伯历见于宿所。午登双乐亭。据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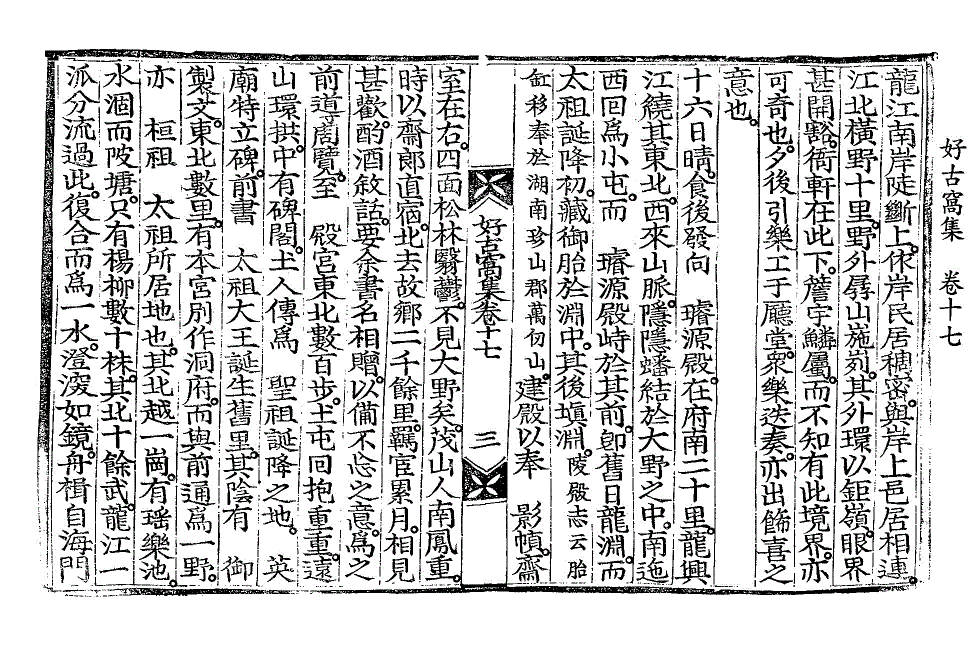 龙江南岸陡断上。依岸民居稠密。与岸上邑居相连。江北横野十里。野外孱山崺峛。其外环以钜岭。眼界甚开豁。衙轩在此下。檐宇鳞属。而不知有此境界。亦可奇也。夕后引乐工于厅堂。众乐迭奏。亦出饰喜之意也。
龙江南岸陡断上。依岸民居稠密。与岸上邑居相连。江北横野十里。野外孱山崺峛。其外环以钜岭。眼界甚开豁。衙轩在此下。檐宇鳞属。而不知有此境界。亦可奇也。夕后引乐工于厅堂。众乐迭奏。亦出饰喜之意也。十六日晴。食后发向 璿源殿。在府南二十里。龙兴江绕其东北。西来山脉。隐隐蟠结于大野之中。南迤西回为小屯。而 璿源殿峙于其前。即旧日龙渊。而太祖诞降初。藏御胎于渊中。其后填渊。(陵殿志云胎缸移奉于湖南珍山郡万仞山。)建殿以奉 影帧。斋室在右。四面松林翳郁。不见大野矣。茂山人南凤重。时以斋郎直宿。北去故乡二千馀里。羁宦累月。相见甚欢。酌酒叙话。要余书名相赠。以备不忘之意。为之前导周览。至 殿宫东北数百步。土屯回抱重重。远山环拱。中有碑阁。土人传为 圣祖诞降之地。 英庙特立碑。前书 太祖大王诞生旧里。其阴有 御制文。东北数里。有本宫别作洞府。而与前通为一野。亦 桓祖 太祖所居地也。其北越一岗。有瑶乐池。水涸而陂塘。只有杨柳数十株。其北十馀武。龙江一派分流过此。复合而为一水。澄深如镜。舟楫自海门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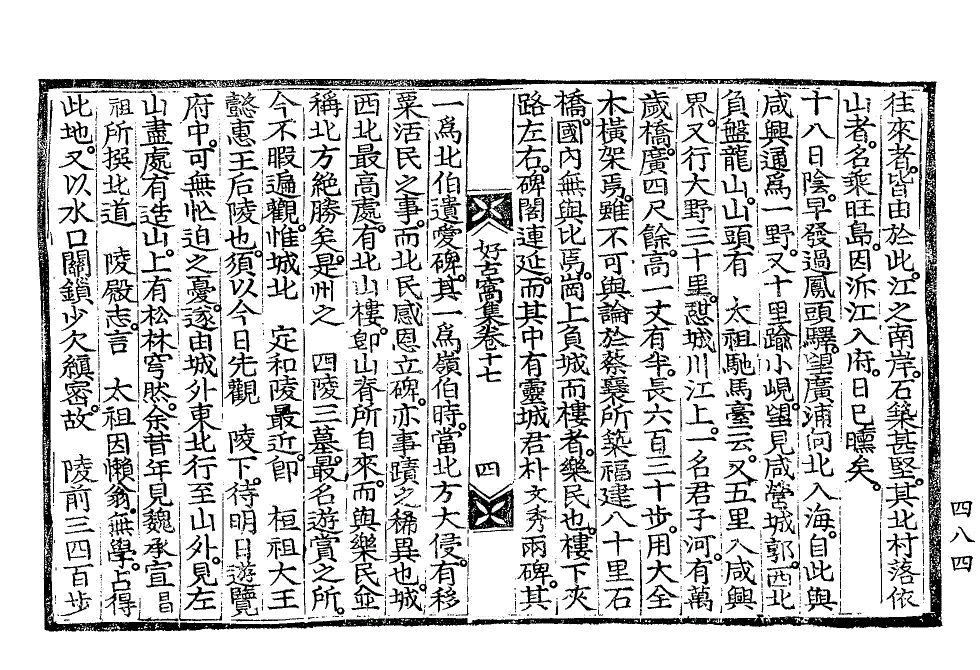 往来者。皆由于此。江之南岸。石筑甚坚。其北村落依山者。名乘旺岛。因溯江入府。日已曛矣。
往来者。皆由于此。江之南岸。石筑甚坚。其北村落依山者。名乘旺岛。因溯江入府。日已曛矣。十八日阴。早发过凤头驿。望广浦向北入海。自此与咸兴通为一野。又十里踰小岘。望见咸营城郭。西北负盘龙山。山头有 太祖驰马台云。又五里入咸兴界。又行大野三十里。憩城川江上。一名君子河。有万岁桥。广四尺馀。高一丈有半。长六百三十步。用大全木横架焉。虽不可与论于蔡襄所筑福建八十里石桥。国内无与比焉。岗上负城而楼者。乐民也。楼下夹路左右。碑阁连延。而其中有灵城君朴(文秀)两碑。其一为北伯遗爱碑。其一为岭伯时。当北方大侵。有移粟活民之事。而北民感恩立碑。亦事迹之稀异也。城西北最高处。有北山楼。即山脊所自来。而与乐民并称北方绝胜矣。是州之 四陵三墓。最名游赏之所。今不暇遍观。惟城北 定和陵最近。即 桓祖大王懿惠王后陵也。须以今日先观 陵下。待明日游览府中。可无忙迫之忧。遂由城外东北行至山外。见左山尽处有造山。上有松林穹然。余昔年见魏承宣(昌祖)所撰北道 陵殿志。言 太祖因懒翁,无学。占得此地。又以水口关锁少欠缜密。故 陵前三四百步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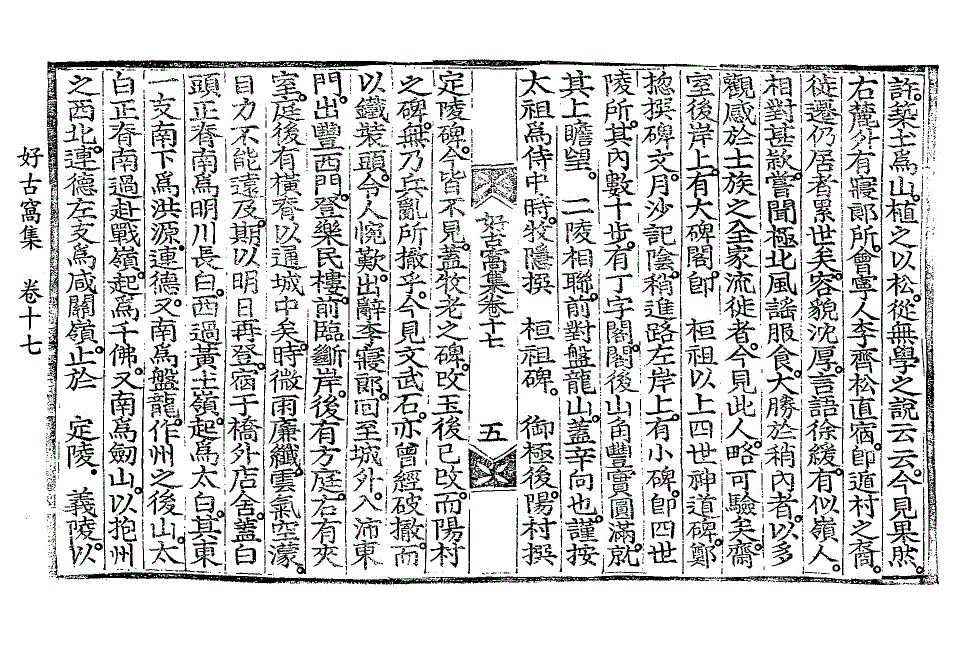 许。筑土为山。植之以松。从无学之说云云。今见果然。右麓外有寝郎所。会宁人李齐松直宿。即遁村之裔。徙迁仍居者累世矣。容貌沈厚。言语徐缓。有似岭人。相对甚款。尝闻极北风谣服食。大胜于稍内者。以多观感于士族之全家流徙者。今见此人。略可验矣。斋室后岸上。有大碑阁。即 桓祖以上四世神道碑。郑揔撰碑文。月沙记阴。稍进路左岸上。有小碑。即四世陵所。其内数十步。有丁字阁。阁后山角丰实圆满。就其上瞻望。 二陵相联。前对盘龙山。盖辛向也。谨按太祖为侍中时。牧隐撰 桓祖碑。 御极后。阳村撰定陵碑。今皆不见。盖牧老之碑。改玉后已改。而阳村之碑。无乃兵乱所撤乎。今见文武石。亦曾经破撤。而以铁装头。令人惋叹。出辞李寝郎。回至城外。入沛东门。出丰西门。登乐民楼。前临断岸。后有方庭。右有夹室。庭后有横脊以通城中矣。时微雨廉纤。云气空濛。目力不能远及。期以明日再登。宿于桥外店舍。盖白头正脊南为明川长白。西过黄土岭。起为太白。其东一支南下为洪源,连德。又南为盘龙。作州之后山。太白正脊南过赴战岭。起为千佛。又南为剑山。以抱州之西北。连德左支为咸关岭。止于 定陵, 义陵。以
许。筑土为山。植之以松。从无学之说云云。今见果然。右麓外有寝郎所。会宁人李齐松直宿。即遁村之裔。徙迁仍居者累世矣。容貌沈厚。言语徐缓。有似岭人。相对甚款。尝闻极北风谣服食。大胜于稍内者。以多观感于士族之全家流徙者。今见此人。略可验矣。斋室后岸上。有大碑阁。即 桓祖以上四世神道碑。郑揔撰碑文。月沙记阴。稍进路左岸上。有小碑。即四世陵所。其内数十步。有丁字阁。阁后山角丰实圆满。就其上瞻望。 二陵相联。前对盘龙山。盖辛向也。谨按太祖为侍中时。牧隐撰 桓祖碑。 御极后。阳村撰定陵碑。今皆不见。盖牧老之碑。改玉后已改。而阳村之碑。无乃兵乱所撤乎。今见文武石。亦曾经破撤。而以铁装头。令人惋叹。出辞李寝郎。回至城外。入沛东门。出丰西门。登乐民楼。前临断岸。后有方庭。右有夹室。庭后有横脊以通城中矣。时微雨廉纤。云气空濛。目力不能远及。期以明日再登。宿于桥外店舍。盖白头正脊南为明川长白。西过黄土岭。起为太白。其东一支南下为洪源,连德。又南为盘龙。作州之后山。太白正脊南过赴战岭。起为千佛。又南为剑山。以抱州之西北。连德左支为咸关岭。止于 定陵, 义陵。以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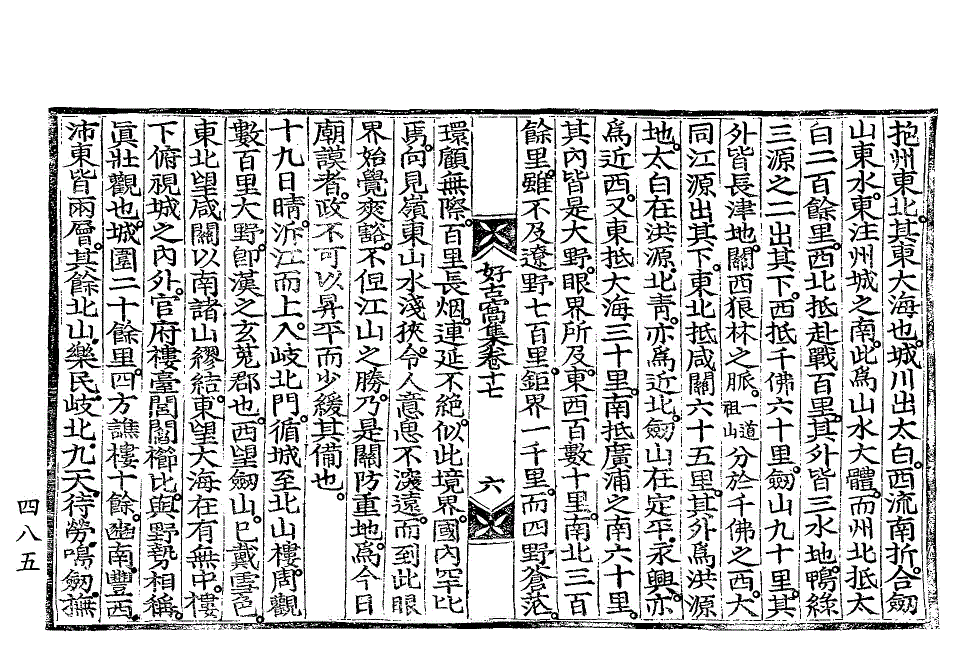 抱州东北。其东大海也。城川出太白。西流南折。合剑山东水。东注州城之南。此为山水大体。而州北抵太白二百馀里。西北抵赴战百里。其外皆三水地。鸭绿三源之二出其下。西抵千佛六十里。剑山九十里。其外皆长津地。关西狼林之脉。(一道祖山。)分于千佛之西。大同江源出其下。东北抵咸关六十五里。其外为洪源地。太白在洪源,北青。亦为近北。剑山在定平,永兴。亦为近西。又东抵大海三十里。南抵广浦之南六十里。其内皆是大野。眼界所及。东西百数十里。南北三百馀里。虽不及辽野七百里。钜界一千里。而四野苍茫。环顾无际。百里长烟。连延不绝。似此境界。国内罕比焉。向见岭东山水浅狭。令人意思不深远。而到此眼界始觉爽豁。不但江山之胜。乃是关防重地。为今日庙谟者。政不可以升平而少缓其备也。
抱州东北。其东大海也。城川出太白。西流南折。合剑山东水。东注州城之南。此为山水大体。而州北抵太白二百馀里。西北抵赴战百里。其外皆三水地。鸭绿三源之二出其下。西抵千佛六十里。剑山九十里。其外皆长津地。关西狼林之脉。(一道祖山。)分于千佛之西。大同江源出其下。东北抵咸关六十五里。其外为洪源地。太白在洪源,北青。亦为近北。剑山在定平,永兴。亦为近西。又东抵大海三十里。南抵广浦之南六十里。其内皆是大野。眼界所及。东西百数十里。南北三百馀里。虽不及辽野七百里。钜界一千里。而四野苍茫。环顾无际。百里长烟。连延不绝。似此境界。国内罕比焉。向见岭东山水浅狭。令人意思不深远。而到此眼界始觉爽豁。不但江山之胜。乃是关防重地。为今日庙谟者。政不可以升平而少缓其备也。十九日晴。溯江而上。入岐北门。循城至北山楼。周观数百里大野。即汉之玄菟郡也。西望剑山。已戴雪色。东北望咸关以南诸山缪结。东望大海在有无中。楼下俯视城之内外。官府楼台闾阎栉比。与野势相称。真壮观也。城围二十馀里。四方谯楼十馀。豳南,丰西,沛东皆两层。其馀北山,乐民,岐北,九天,待劳,鸣剑,抚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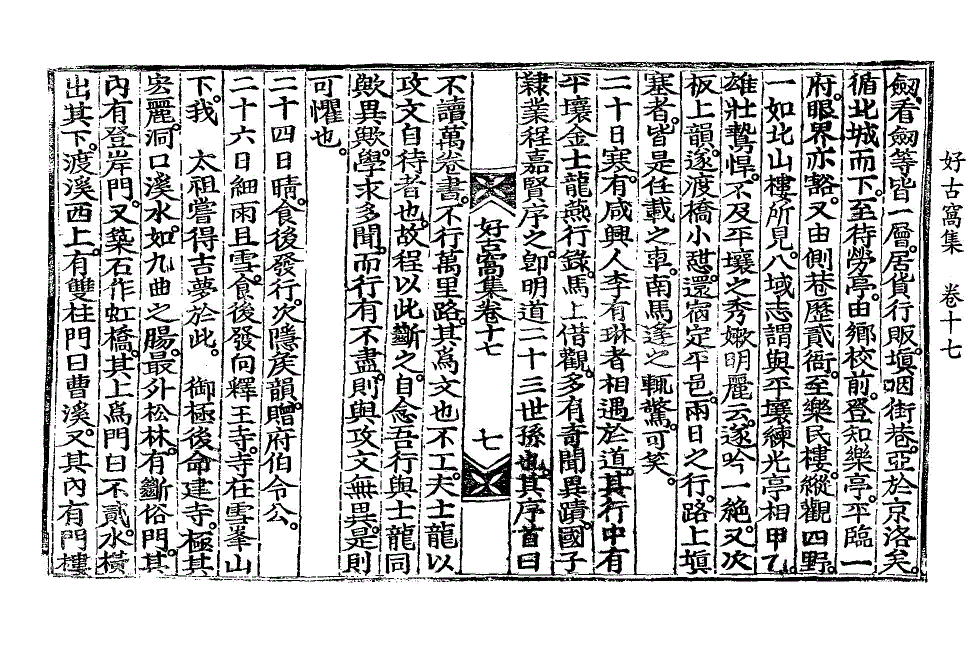 剑,看剑等皆一层。居货行贩。填咽街巷。亚于京洛矣。循北城而下。至待劳亭。由乡校前。登知乐亭。平临一府。眼界亦豁。又由侧巷历贰衙。至乐民楼。纵观四野。一如北山楼所见。八域志谓与平壤练光亭相甲乙。雄壮鸷悍。不及平壤之秀嫩明丽云。遂吟一绝。又次板上韵。遂渡桥小憩。还宿定平邑。两日之行。路上填塞者。皆是任载之车。南马逢之辄惊。可笑。
剑,看剑等皆一层。居货行贩。填咽街巷。亚于京洛矣。循北城而下。至待劳亭。由乡校前。登知乐亭。平临一府。眼界亦豁。又由侧巷历贰衙。至乐民楼。纵观四野。一如北山楼所见。八域志谓与平壤练光亭相甲乙。雄壮鸷悍。不及平壤之秀嫩明丽云。遂吟一绝。又次板上韵。遂渡桥小憩。还宿定平邑。两日之行。路上填塞者。皆是任载之车。南马逢之辄惊。可笑。二十日寒。有咸兴人李有琳者相遇于道。其行中有平壤金士龙燕行录。马上借观。多有奇闻异迹。国子隶业程嘉贤序之。即明道二十三世孙也。其序首曰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其为文也不工。夫士龙以攻文自待者也。故程以此断之。自念吾行与士龙同欤异欤。学求多闻。而行有不尽。则与攻文无异。是则可惧也。
二十四日晴。食后发行。次隐侯韵。赠府伯令公。
二十六日细雨且雪。食后发向释王寺。寺在雪峰山下。我 太祖尝得吉梦于此。 御极后命建寺。极其宏丽。洞口溪水。如九曲之肠。最外松林。有断俗门。其内有登岸门。又筑石作虹桥。其上为门曰不贰。水横出其下。渡溪西上。有双柱门曰曹溪。又其内有门楼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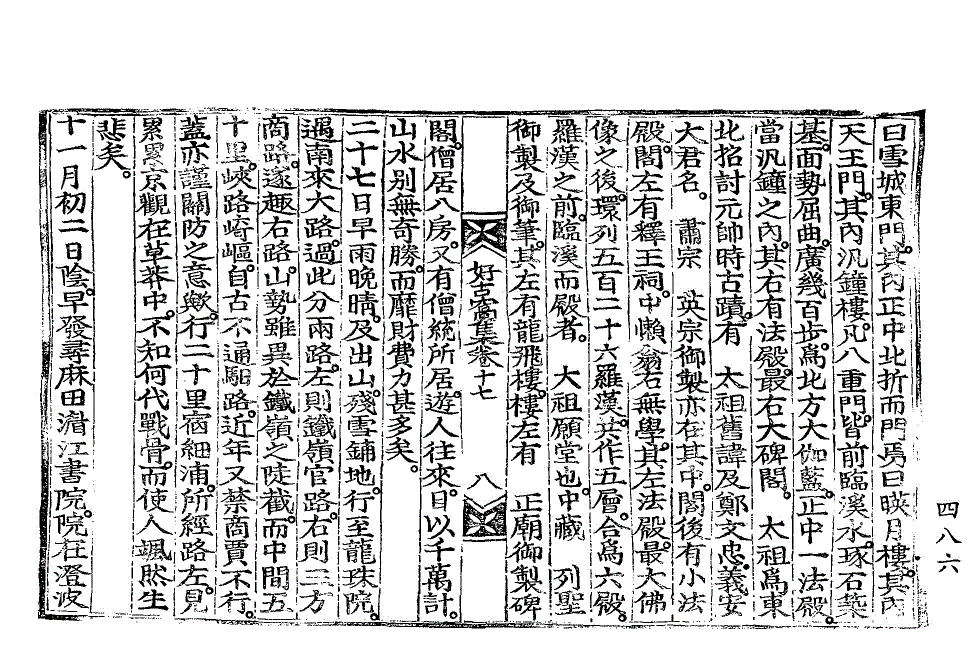 曰雪城东门。其内正中北折而门焉曰映月楼。其内天王门。其内汎钟楼。凡八重门。皆前临溪水。琢石筑基。面势屈曲。广几百步。为北方大伽蓝。正中一法殿。当汎钟之内。其右有法殿。最右大碑阁。 太祖为东北招讨元帅时古迹。有 太祖旧讳及郑文忠,义安大君名。 肃宗 英宗御制亦在其中。阁后有小法殿。阁左有释王祠。中懒翁右无学。其左法殿。最大佛像之后。环列五百二十六罗汉。共作五层。合为六殿。罗汉之前。临溪而殿者。 大祖愿堂也。中藏 列圣御制及御笔。其左有龙飞楼。楼左有 正庙御制碑阁。僧居八房。又有僧统所居。游人往来。日以千万计。山水别无奇胜。而靡财费力甚多矣。
曰雪城东门。其内正中北折而门焉曰映月楼。其内天王门。其内汎钟楼。凡八重门。皆前临溪水。琢石筑基。面势屈曲。广几百步。为北方大伽蓝。正中一法殿。当汎钟之内。其右有法殿。最右大碑阁。 太祖为东北招讨元帅时古迹。有 太祖旧讳及郑文忠,义安大君名。 肃宗 英宗御制亦在其中。阁后有小法殿。阁左有释王祠。中懒翁右无学。其左法殿。最大佛像之后。环列五百二十六罗汉。共作五层。合为六殿。罗汉之前。临溪而殿者。 大祖愿堂也。中藏 列圣御制及御笔。其左有龙飞楼。楼左有 正庙御制碑阁。僧居八房。又有僧统所居。游人往来。日以千万计。山水别无奇胜。而靡财费力甚多矣。二十七日早雨晚晴。及出山。残雪铺地。行至龙珠院。遇南来大路。过此分两路。左则铁岭官路。右则三方商路。遂趣右路。山势虽异于铁岭之陡截。而中间五十里。峡路崎岖。自古不通驲路。近年又禁商贾不行。盖亦谨关防之意欤。行二十里宿细浦。所经路左。见累累京观在草莽中。不知何代战骨。而使人飒然生悲矣。
十一月初二日阴。早发寻麻田湄江书院。院在澄波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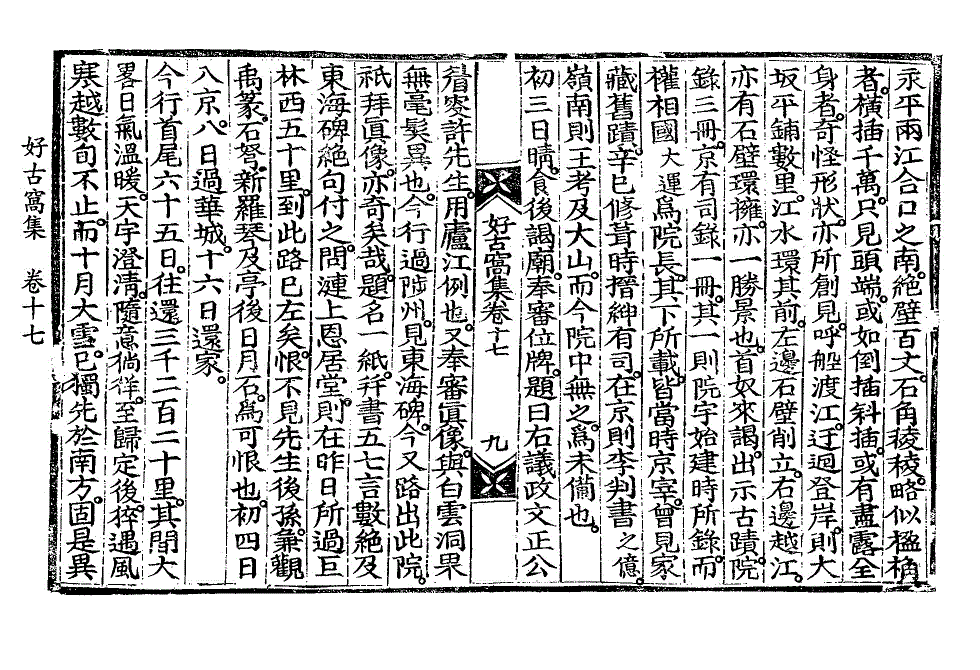 永平两江合口之南。绝壁百丈。石角棱棱。略似楹桷者。横插千万。只见头端。或如倒插斜插。或有尽露全身者。奇怪形状。亦所创见。呼船渡江。迂回登岸。则大坂平铺数里。江水环其前。左边石壁削立。右边越江。亦有石壁环拥。亦一胜景也。首奴来谒。出示古迹。院录三册。京有司录一册。其一则院宇始建时所录。而权相国(大运)为院长。其下所载。皆当时京宰。曾见家藏旧迹。辛巳修葺时搢绅有司。在京则李判书(之亿)。岭南则王考及大山。而今院中无之。为未备也。
永平两江合口之南。绝壁百丈。石角棱棱。略似楹桷者。横插千万。只见头端。或如倒插斜插。或有尽露全身者。奇怪形状。亦所创见。呼船渡江。迂回登岸。则大坂平铺数里。江水环其前。左边石壁削立。右边越江。亦有石壁环拥。亦一胜景也。首奴来谒。出示古迹。院录三册。京有司录一册。其一则院宇始建时所录。而权相国(大运)为院长。其下所载。皆当时京宰。曾见家藏旧迹。辛巳修葺时搢绅有司。在京则李判书(之亿)。岭南则王考及大山。而今院中无之。为未备也。初三日晴。食后谒庙。奉审位牌。题曰右议政文正公眉叟许先生。用庐江例也。又奉审真像。与白云洞果无毫发异也。今行过陟州。见东海碑。今又路出此院。祇拜真像。亦奇矣哉。题名一纸。并书五七言数绝及东海碑绝句付之。问涟上恩居堂。则在昨日所过巨林西五十里。到此路已左矣。恨不见先生后孙。兼观禹篆,石弩,新罗琴及亭后日月石。为可恨也。初四日入京。八日过华城。十六日还家。
今行首尾六十五日。往还三千二百二十里。其间大略日气温暖。天宇澄清。随意徜徉。至归定后。猝遇风寒越数旬不止。而十月大雪。已独先于南方。固是异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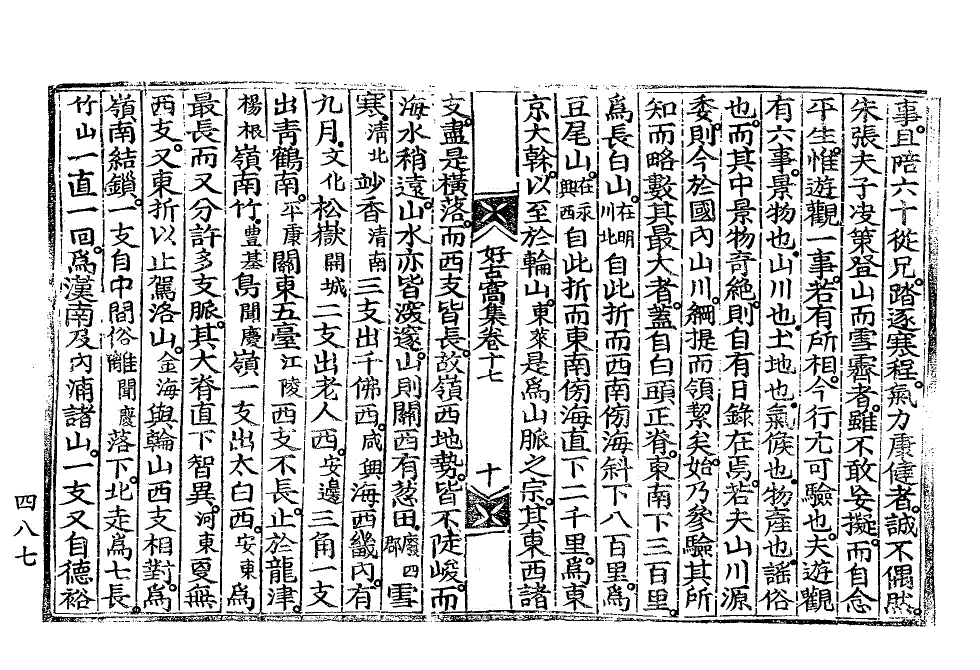 事。且陪六十从兄。踏逐寒程。气力康健者。诚不偶然。朱张夫子决策登山而雪霁者。虽不敢妄拟。而自念平生。惟游观一事。若有所相。今行尤可验也。夫游观有六事。景物也,山川也,土地也,气候也,物产也,谣俗也。而其中景物奇绝。则自有日录在焉。若夫山川源委。则今于国内山川。纲提而领絜矣。始乃参验其所知而略数其最大者。盖自白头正脊。东南下三百里。为长白山。(在明川北。)自此折而西南傍海斜下八百里。为豆尾山。(在永兴西。)自此折而东南傍海直下二千里。为东京大干。以至于轮山。(东莱。)是为山脉之宗。其东西诸支。尽是横落。而西支皆长。故岭西地势。皆不陡峻。而海水稍远。山水亦皆深邃。山则关西有葱田(废四郡),雪寒(清北),妙香(清南)三支出千佛西(咸兴)。海西畿内。有九月(文化),松岳(开城)二支出老人西(安边)。三角一支出青鹤南(平康)。关东五台(江陵)西支不长。止于龙津(杨根)。岭南竹(礼基),鸟(闻庆)岭一支出太白西(安东)。为最长而又分许多支脉。其大脊直下智异(河东)。更无西支。又东折以止驾洛山(金海)。与轮山西支相对。为岭南结锁。一支自中间俗离(闻庆)落下。北走为七长(竹山)。一直一回。为汉南及内浦诸山。一支又自德裕
事。且陪六十从兄。踏逐寒程。气力康健者。诚不偶然。朱张夫子决策登山而雪霁者。虽不敢妄拟。而自念平生。惟游观一事。若有所相。今行尤可验也。夫游观有六事。景物也,山川也,土地也,气候也,物产也,谣俗也。而其中景物奇绝。则自有日录在焉。若夫山川源委。则今于国内山川。纲提而领絜矣。始乃参验其所知而略数其最大者。盖自白头正脊。东南下三百里。为长白山。(在明川北。)自此折而西南傍海斜下八百里。为豆尾山。(在永兴西。)自此折而东南傍海直下二千里。为东京大干。以至于轮山。(东莱。)是为山脉之宗。其东西诸支。尽是横落。而西支皆长。故岭西地势。皆不陡峻。而海水稍远。山水亦皆深邃。山则关西有葱田(废四郡),雪寒(清北),妙香(清南)三支出千佛西(咸兴)。海西畿内。有九月(文化),松岳(开城)二支出老人西(安边)。三角一支出青鹤南(平康)。关东五台(江陵)西支不长。止于龙津(杨根)。岭南竹(礼基),鸟(闻庆)岭一支出太白西(安东)。为最长而又分许多支脉。其大脊直下智异(河东)。更无西支。又东折以止驾洛山(金海)。与轮山西支相对。为岭南结锁。一支自中间俗离(闻庆)落下。北走为七长(竹山)。一直一回。为汉南及内浦诸山。一支又自德裕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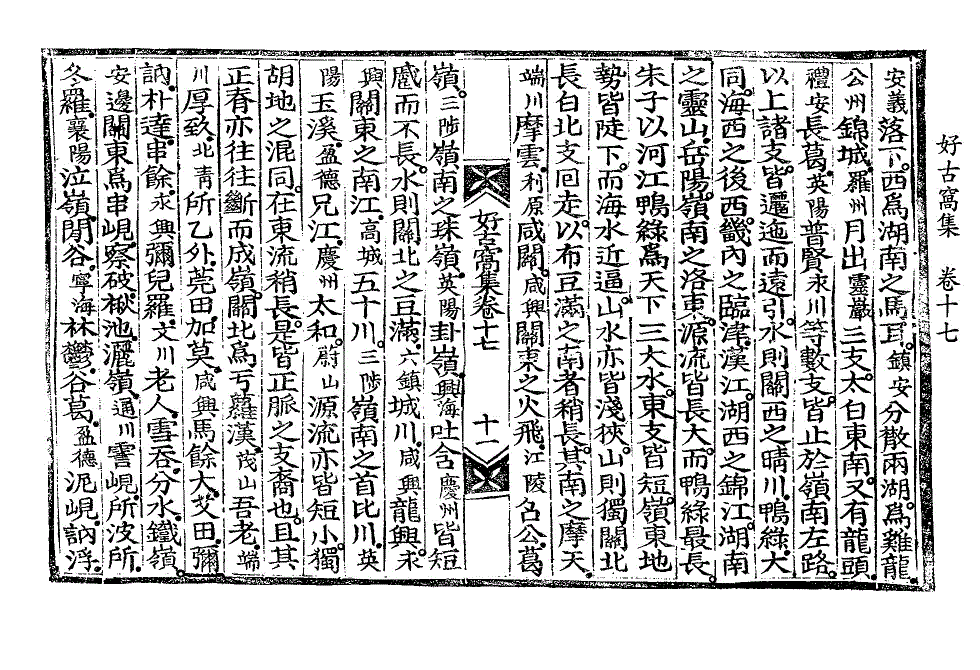 (安义)落下。西为湖南之马耳(镇安)。分散两湖。为鸡龙(公州),锦城(罗州),月出(灵岩)三支。太白东南。又有龙头(礼安),长葛(英阳),普贤(永川)等数支。皆止于岭南左路。以上诸支。皆逦迤而远引。水则关西之晴川,鸭绿,大同。海西之后西。畿内之临津,汉江。湖西之锦江。湖南之灵山,岳阳。岭南之洛东。源流皆长大。而鸭绿最长。朱子以河江鸭绿为天下三大水。东支皆短。岭东地势皆陡下。而海水近逼。山水亦皆浅狭。山则独关北长白北支回走。以布豆满之南者稍长。其南之摩天(端川),摩云(利原),咸关(咸兴)。关东之火飞(江陵),召公,葛岭(三陟)。岭南之珠岭(英阳),卦岭(兴海),吐含(庆州)皆短蹙而不长。水则关北之豆满(六镇),城川(咸兴),龙兴(永兴)。关东之南江(高城),五十川(三陟)。岭南之首比川(英阳),玉溪(盈德),兄江(庆州),太和(蔚山)。源流亦皆短小。独胡地之混同。在东流稍长。是皆正脉之支裔也。且其正脊亦往往断而成岭。关北为于萝汉(茂山),吾老(端川),厚致(北青),所乙外,莞田,加莫(咸兴),马馀大,艾田,弥讷,朴达,串馀(永兴),弥儿罗(文川),老人,雪吞,分水,铁岭(安边)。关东为串岘,察破,楸池,洒岭(通川),霅岘,所波所,冬罗(襄阳),泣岭,閒谷(宁海),林郁,谷葛(盈德),泥岘,讷浮
(安义)落下。西为湖南之马耳(镇安)。分散两湖。为鸡龙(公州),锦城(罗州),月出(灵岩)三支。太白东南。又有龙头(礼安),长葛(英阳),普贤(永川)等数支。皆止于岭南左路。以上诸支。皆逦迤而远引。水则关西之晴川,鸭绿,大同。海西之后西。畿内之临津,汉江。湖西之锦江。湖南之灵山,岳阳。岭南之洛东。源流皆长大。而鸭绿最长。朱子以河江鸭绿为天下三大水。东支皆短。岭东地势皆陡下。而海水近逼。山水亦皆浅狭。山则独关北长白北支回走。以布豆满之南者稍长。其南之摩天(端川),摩云(利原),咸关(咸兴)。关东之火飞(江陵),召公,葛岭(三陟)。岭南之珠岭(英阳),卦岭(兴海),吐含(庆州)皆短蹙而不长。水则关北之豆满(六镇),城川(咸兴),龙兴(永兴)。关东之南江(高城),五十川(三陟)。岭南之首比川(英阳),玉溪(盈德),兄江(庆州),太和(蔚山)。源流亦皆短小。独胡地之混同。在东流稍长。是皆正脉之支裔也。且其正脊亦往往断而成岭。关北为于萝汉(茂山),吾老(端川),厚致(北青),所乙外,莞田,加莫(咸兴),马馀大,艾田,弥讷,朴达,串馀(永兴),弥儿罗(文川),老人,雪吞,分水,铁岭(安边)。关东为串岘,察破,楸池,洒岭(通川),霅岘,所波所,冬罗(襄阳),泣岭,閒谷(宁海),林郁,谷葛(盈德),泥岘,讷浮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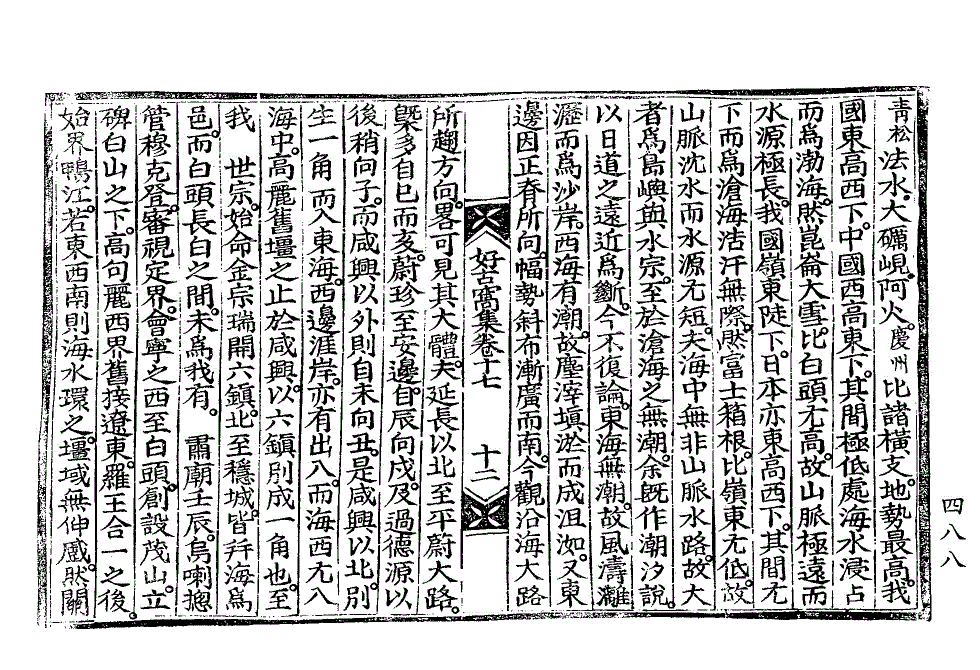 (青松),法水,大砺岘,阿火(庆州)。比诸横支。地势最高。我国东高西下。中国西高东下。其间极低处海水浸占而为渤海。然昆崙大雪。比白头尤高。故山脉极远而水源极长。我国岭东陡下。日本亦东高西下。其间尤下而为沧海浩汗无际。然富士箱根。比岭东尤低。故山脉沈水而水源尤短。夫海中无非山脉水路。故大者为岛屿与水宗。至于沧海之无潮。余既作潮汐说。以日道之远近为断。今不复论。东海无潮。故风涛漓沥而为沙岸。西海有潮。故尘滓填淤而成沮洳。又东边因正脊所向。幅势斜布渐广而南。今观沿海大路所趋方向。略可见其大体。夫延长以北至平蔚大路。槩多自巳而亥。蔚珍至安边。自辰向戌。及过德源以后稍向子。而咸兴以外则自未向丑。是咸兴以北。别生一角而入东海。西边涯岸。亦有出入。而海西尤入海中。高丽旧疆之止于咸兴。以六镇别成一角也。至我 世宗。始命金宗瑞开六镇。北至稳城。皆并海为邑。而白头长白之间。未为我有。 肃庙壬辰。乌喇总管穆克登。审视定界。会宁之西至白头。创设茂山。立碑白山之下。高句丽西界旧接辽东。罗王合一之后。始界鸭江。若东西南则海水环之。疆域无伸蹙。然关
(青松),法水,大砺岘,阿火(庆州)。比诸横支。地势最高。我国东高西下。中国西高东下。其间极低处海水浸占而为渤海。然昆崙大雪。比白头尤高。故山脉极远而水源极长。我国岭东陡下。日本亦东高西下。其间尤下而为沧海浩汗无际。然富士箱根。比岭东尤低。故山脉沈水而水源尤短。夫海中无非山脉水路。故大者为岛屿与水宗。至于沧海之无潮。余既作潮汐说。以日道之远近为断。今不复论。东海无潮。故风涛漓沥而为沙岸。西海有潮。故尘滓填淤而成沮洳。又东边因正脊所向。幅势斜布渐广而南。今观沿海大路所趋方向。略可见其大体。夫延长以北至平蔚大路。槩多自巳而亥。蔚珍至安边。自辰向戌。及过德源以后稍向子。而咸兴以外则自未向丑。是咸兴以北。别生一角而入东海。西边涯岸。亦有出入。而海西尤入海中。高丽旧疆之止于咸兴。以六镇别成一角也。至我 世宗。始命金宗瑞开六镇。北至稳城。皆并海为邑。而白头长白之间。未为我有。 肃庙壬辰。乌喇总管穆克登。审视定界。会宁之西至白头。创设茂山。立碑白山之下。高句丽西界旧接辽东。罗王合一之后。始界鸭江。若东西南则海水环之。疆域无伸蹙。然关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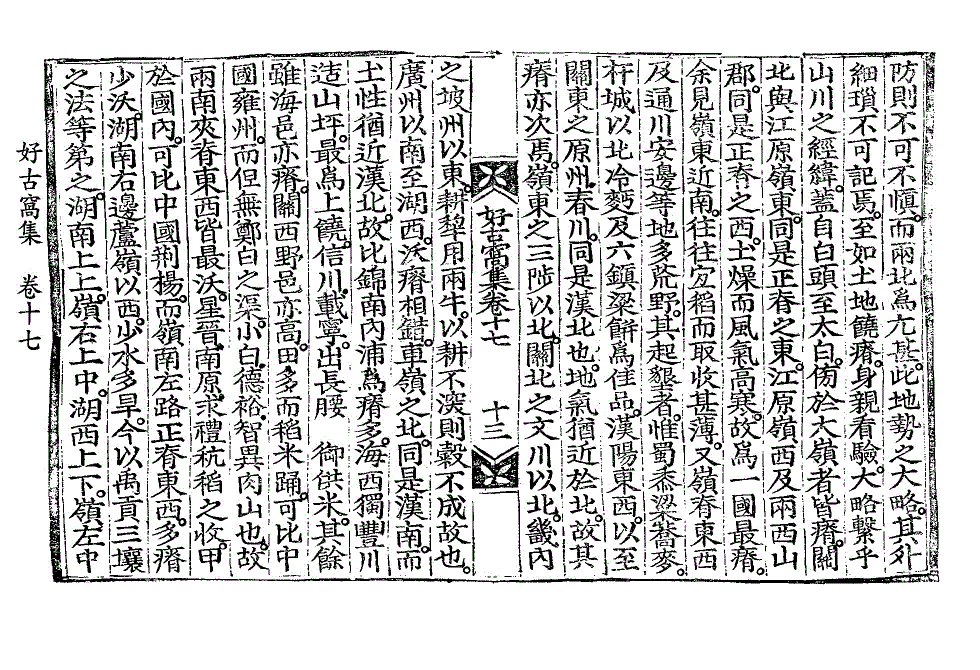 防则不可不慎。而两北为尤甚。此地势之大略。其外细琐不可记焉。至如土地饶瘠。身亲看验。大略系乎山川之经纬。盖自白头至太白。傍于大岭者皆瘠。关北与江原岭东。同是正脊之东。江原岭西及两西山郡。同是正脊之西。土燥而风气高寒。故为一国最瘠。余见岭东近南。往往宜稻而取收甚薄。又岭脊东西及通川安边等地多荒野。其起垦者。惟蜀黍粱荞麦。杆城以北冷面及六镇粱饼为佳品。汉阳东西。以至关东之原州,春川。同是汉北也。地气犹近于北。故其瘠亦次焉。岭东之三陟以北。关北之文川以北。畿内之坡州以东。耕犁用两牛。以耕不深则谷不成故也。广州以南至湖西。沃瘠相错。车岭之北。同是汉南。而土性犹近汉北。故比锦南内浦为瘠多。海西独丰川造山坪。最为上饶。信川,载宁。出长腰 御供米。其馀虽海邑亦瘠。关西野邑亦高。田多而稻米踊。可比中国雍州。而但无郑白之渠。小白,德裕,智异肉山也。故两南夹脊东西皆最沃。星晋,南原,求礼粳稻之收。甲于国内。可比中国荆杨。而岭南左路正脊东西。多瘠少沃。湖南右边芦岭以西。少水多旱。今以禹贡三壤之法等第之。湖南上上。岭右上中。湖西上下。岭左中
防则不可不慎。而两北为尤甚。此地势之大略。其外细琐不可记焉。至如土地饶瘠。身亲看验。大略系乎山川之经纬。盖自白头至太白。傍于大岭者皆瘠。关北与江原岭东。同是正脊之东。江原岭西及两西山郡。同是正脊之西。土燥而风气高寒。故为一国最瘠。余见岭东近南。往往宜稻而取收甚薄。又岭脊东西及通川安边等地多荒野。其起垦者。惟蜀黍粱荞麦。杆城以北冷面及六镇粱饼为佳品。汉阳东西。以至关东之原州,春川。同是汉北也。地气犹近于北。故其瘠亦次焉。岭东之三陟以北。关北之文川以北。畿内之坡州以东。耕犁用两牛。以耕不深则谷不成故也。广州以南至湖西。沃瘠相错。车岭之北。同是汉南。而土性犹近汉北。故比锦南内浦为瘠多。海西独丰川造山坪。最为上饶。信川,载宁。出长腰 御供米。其馀虽海邑亦瘠。关西野邑亦高。田多而稻米踊。可比中国雍州。而但无郑白之渠。小白,德裕,智异肉山也。故两南夹脊东西皆最沃。星晋,南原,求礼粳稻之收。甲于国内。可比中国荆杨。而岭南左路正脊东西。多瘠少沃。湖南右边芦岭以西。少水多旱。今以禹贡三壤之法等第之。湖南上上。岭右上中。湖西上下。岭左中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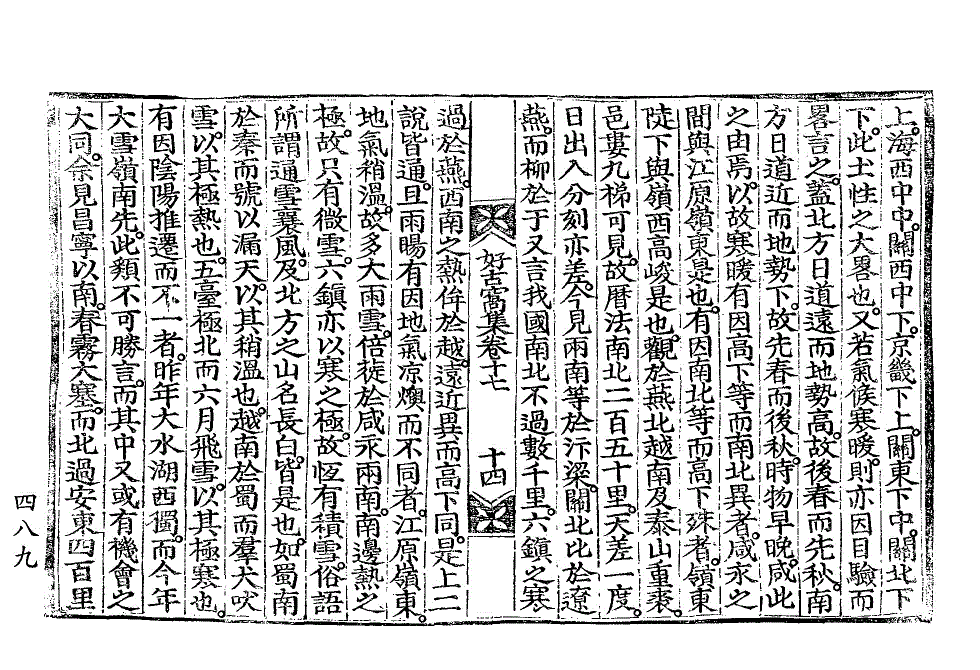 上。海西中中。关西中下。京畿下上。关东下中。关北下下。此土性之大略也。又若气候寒暖。则亦因目验而略言之。盖北方日道远而地势高。故后春而先秋。南方日道近而地势下。故先春而后秋。时物早晚。咸此之由焉。以故寒暖有因高下等而南北异者。咸永之间与江原岭东是也。有因南北等而高下殊者。岭东陡下与岭西高峻是也。观于燕北越南及泰山重裘。邑娄九梯可见。故历法南北二百五十里。天差一度。日出入分刻亦差。今见两南等于汴梁。关北比于辽燕。而柳于于又言我国南北不过数千里。六镇之寒过于燕。西南之热侔于越。远近异而高下同。是上二说皆通。且雨旸有因地气凉燠而不同者。江原岭东。地气稍温。故多大雨雪。倍蓰于咸永两南。南边热之极。故只有微雪。六镇亦以寒之极。故恒有积雪。俗语所谓通雪襄风。及北方之山名长白。皆是也。如蜀南于秦而号以漏天。以其稍温也。越南于蜀而群犬吠雪。以其极热也。五台极北而六月飞雪。以其极寒也。有因阴阳推迁而不一者。昨年大水湖西独。而今年大雪岭南先。此类不可胜言。而其中又或有机会之大同。余见昌宁以南。春雾大塞。而北过安东四百里
上。海西中中。关西中下。京畿下上。关东下中。关北下下。此土性之大略也。又若气候寒暖。则亦因目验而略言之。盖北方日道远而地势高。故后春而先秋。南方日道近而地势下。故先春而后秋。时物早晚。咸此之由焉。以故寒暖有因高下等而南北异者。咸永之间与江原岭东是也。有因南北等而高下殊者。岭东陡下与岭西高峻是也。观于燕北越南及泰山重裘。邑娄九梯可见。故历法南北二百五十里。天差一度。日出入分刻亦差。今见两南等于汴梁。关北比于辽燕。而柳于于又言我国南北不过数千里。六镇之寒过于燕。西南之热侔于越。远近异而高下同。是上二说皆通。且雨旸有因地气凉燠而不同者。江原岭东。地气稍温。故多大雨雪。倍蓰于咸永两南。南边热之极。故只有微雪。六镇亦以寒之极。故恒有积雪。俗语所谓通雪襄风。及北方之山名长白。皆是也。如蜀南于秦而号以漏天。以其稍温也。越南于蜀而群犬吠雪。以其极热也。五台极北而六月飞雪。以其极寒也。有因阴阳推迁而不一者。昨年大水湖西独。而今年大雪岭南先。此类不可胜言。而其中又或有机会之大同。余见昌宁以南。春雾大塞。而北过安东四百里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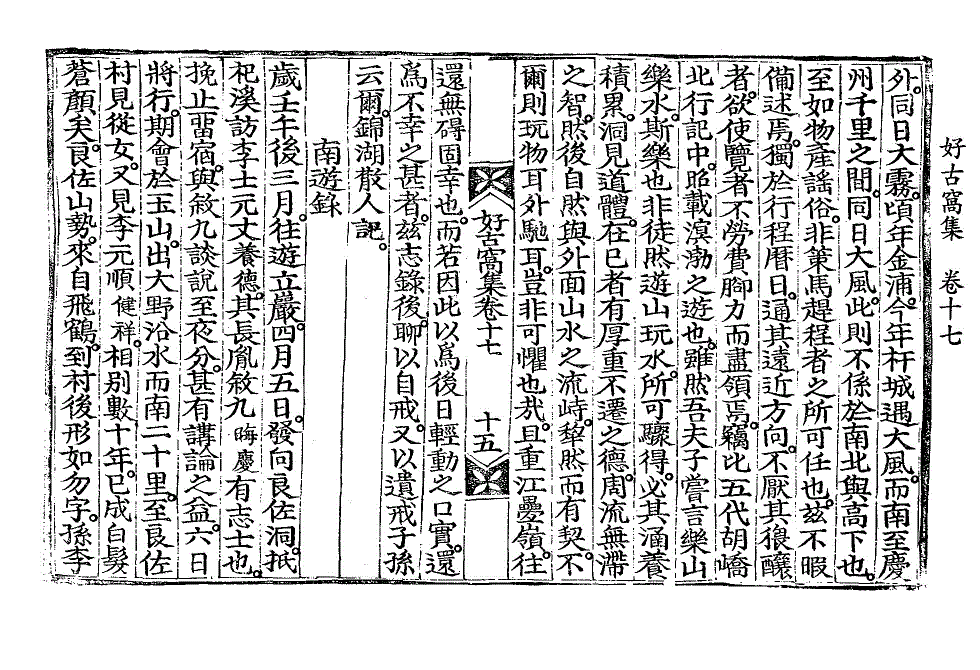 外。同日大雾。顷年金浦。今年杆城遇大风。而南至庆州千里之间。同日大风。此则不系于南北与高下也。至如物产谣俗。非策马赶程者之所可任也。玆不暇备述焉。独于行程历日。通其远近方向。不厌其猥酿者。欲使览者。不劳费脚力而尽领焉。窃比五代胡峤北行记中。昭载溟渤之游也。虽然吾夫子尝言乐山乐水。斯乐也非徒然游山玩水。所可骤得。必其涵养积累。洞见道体。在己者有厚重不迁之德。周流无滞之智。然后自然与外面山水之流峙。犁然而有契。不尔则玩物耳外驰耳。岂非可惧也哉。且重江叠岭。往还无碍固幸也。而若因此以为后日轻动之口实。还为不幸之甚者。玆志录后。聊以自戒。又以遗戒子孙云尔。锦湖散人记。
外。同日大雾。顷年金浦。今年杆城遇大风。而南至庆州千里之间。同日大风。此则不系于南北与高下也。至如物产谣俗。非策马赶程者之所可任也。玆不暇备述焉。独于行程历日。通其远近方向。不厌其猥酿者。欲使览者。不劳费脚力而尽领焉。窃比五代胡峤北行记中。昭载溟渤之游也。虽然吾夫子尝言乐山乐水。斯乐也非徒然游山玩水。所可骤得。必其涵养积累。洞见道体。在己者有厚重不迁之德。周流无滞之智。然后自然与外面山水之流峙。犁然而有契。不尔则玩物耳外驰耳。岂非可惧也哉。且重江叠岭。往还无碍固幸也。而若因此以为后日轻动之口实。还为不幸之甚者。玆志录后。聊以自戒。又以遗戒子孙云尔。锦湖散人记。南游录
岁壬午后三月。往游立岩。四月五日。发向良佐洞。抵杞溪访李士元丈(养德)。其长胤叙九(晦庆)有志士也。挽止留宿。与叙九谈说至夜分。甚有讲论之益。六日将行。期会于玉山。出大野沿水而南二十里。至良佐村见从女。又见李元顺(健祥)。相别数十年。已成白发苍颜矣。良佐山势。来自飞鹤。到村后形如勿字。孙李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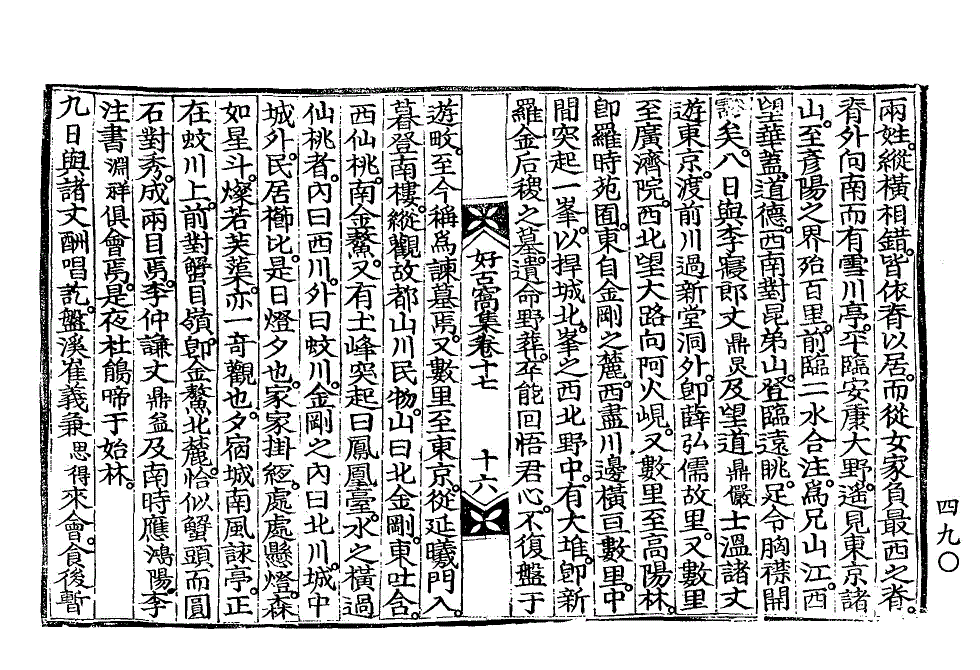 两姓。纵横相错。皆依脊以居。而从女家负最西之脊。脊外向南而有雪川亭。平临安康大野。遥见东京诸山。至彦阳之界殆百里。前临二水合注。为兄山江。西望华盖,道德。西南对昆弟山。登临远眺。足令胸襟开豁矣。八日与李寝郎丈(鼎炅)及望道(鼎俨)士温诸丈游东京。渡前川过新堂洞外。即薛弘儒故里。又数里至广济院。西北望大路向阿火岘。又数里至高阳林。即罗时苑囿。东自金刚之麓。西尽川边横亘数里。中间突起一峰。以捍城北。峰之西北野中。有大堆。即新罗金后稷之墓。遗命野葬。卒能回悟君心。不复盘于游畋。至今称为谏墓焉。又数里至东京。从延曦门入。暮登南楼。纵观故都山川民物。山曰北金刚。东吐含。西仙桃。南金鳌。又有土峰突起曰凤凰台。水之横过仙桃者。内曰西川。外曰蚊川。金刚之内曰北川。城中城外。民居栉比。是日灯夕也。家家挂絙。处处悬灯。森如星斗。灿若芙蕖。亦一奇观也。夕宿城南风咏亭。正在蚊川上。前对蟹目岭。即金鳌北麓。恰似蟹头而圆石对秀。成两目焉。李仲谦丈(鼎益)及南时应(鸿阳),李注书(渊祥)俱会焉。是夜杜鹃啼于始林。
两姓。纵横相错。皆依脊以居。而从女家负最西之脊。脊外向南而有雪川亭。平临安康大野。遥见东京诸山。至彦阳之界殆百里。前临二水合注。为兄山江。西望华盖,道德。西南对昆弟山。登临远眺。足令胸襟开豁矣。八日与李寝郎丈(鼎炅)及望道(鼎俨)士温诸丈游东京。渡前川过新堂洞外。即薛弘儒故里。又数里至广济院。西北望大路向阿火岘。又数里至高阳林。即罗时苑囿。东自金刚之麓。西尽川边横亘数里。中间突起一峰。以捍城北。峰之西北野中。有大堆。即新罗金后稷之墓。遗命野葬。卒能回悟君心。不复盘于游畋。至今称为谏墓焉。又数里至东京。从延曦门入。暮登南楼。纵观故都山川民物。山曰北金刚。东吐含。西仙桃。南金鳌。又有土峰突起曰凤凰台。水之横过仙桃者。内曰西川。外曰蚊川。金刚之内曰北川。城中城外。民居栉比。是日灯夕也。家家挂絙。处处悬灯。森如星斗。灿若芙蕖。亦一奇观也。夕宿城南风咏亭。正在蚊川上。前对蟹目岭。即金鳌北麓。恰似蟹头而圆石对秀。成两目焉。李仲谦丈(鼎益)及南时应(鸿阳),李注书(渊祥)俱会焉。是夜杜鹃啼于始林。九日与诸丈酬唱讫。盘溪崔义兼(思得)来会。食后暂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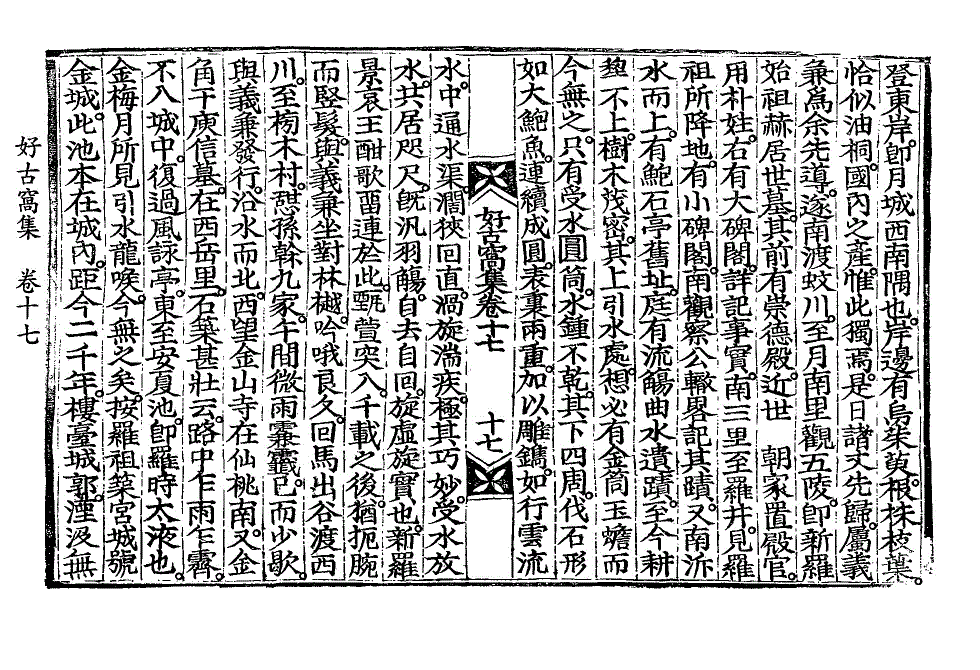 登东岸。即月城西南隅也。岸边有乌茱萸。根株枝叶。恰似油桐。国内之产。惟此独焉。是日诸丈先归。属义兼为余先导。遂南渡蚊川。至月南里观五陵。即新罗始祖赫居世墓。其前有崇德殿。近世 朝家置殿官。用朴姓。右有大碑阁。详记事实。南三里至罗井。见罗祖所降地。有小碑阁。南观察公辙略记其迹。又南溯水而上。有鲍石亭旧址。庭有流觞曲水遗迹。至今耕犁不上。树木茂密。其上引水处。想必有金筒玉蟾而今无之。只有受水圆筒。水钟不乾。其下四周。伐石形如大鲍鱼。连续成圆。表里两重。加以雕镌。如行云流水。中通水渠。阔狭回直。涡旋湍疾。极其巧妙。受水放水。共居咫尺。既汎羽觞。自去自回。旋虚旋实也。新罗景哀王酣歌留连于此。甄萱突入。千载之后。犹扼腕而竖发。与义兼坐对林樾。吟哦良久。回马出谷渡西川。至榜木村。憩孙干九家。午间微雨𩄡𩆷。已而少歇。与义兼发行。沿水而北。西望金山寺在仙桃南。又金角干庾信墓。在西岳里。石筑甚壮云。路中乍雨乍霁。不入城中。复过风咏亭。东至安夏池。即罗时太液也。金梅月所见引水龙喉。今无之矣。按罗祖筑宫城号金城。此池本在城内。距今二千年。楼台城郭。湮没无
登东岸。即月城西南隅也。岸边有乌茱萸。根株枝叶。恰似油桐。国内之产。惟此独焉。是日诸丈先归。属义兼为余先导。遂南渡蚊川。至月南里观五陵。即新罗始祖赫居世墓。其前有崇德殿。近世 朝家置殿官。用朴姓。右有大碑阁。详记事实。南三里至罗井。见罗祖所降地。有小碑阁。南观察公辙略记其迹。又南溯水而上。有鲍石亭旧址。庭有流觞曲水遗迹。至今耕犁不上。树木茂密。其上引水处。想必有金筒玉蟾而今无之。只有受水圆筒。水钟不乾。其下四周。伐石形如大鲍鱼。连续成圆。表里两重。加以雕镌。如行云流水。中通水渠。阔狭回直。涡旋湍疾。极其巧妙。受水放水。共居咫尺。既汎羽觞。自去自回。旋虚旋实也。新罗景哀王酣歌留连于此。甄萱突入。千载之后。犹扼腕而竖发。与义兼坐对林樾。吟哦良久。回马出谷渡西川。至榜木村。憩孙干九家。午间微雨𩄡𩆷。已而少歇。与义兼发行。沿水而北。西望金山寺在仙桃南。又金角干庾信墓。在西岳里。石筑甚壮云。路中乍雨乍霁。不入城中。复过风咏亭。东至安夏池。即罗时太液也。金梅月所见引水龙喉。今无之矣。按罗祖筑宫城号金城。此池本在城内。距今二千年。楼台城郭。湮没无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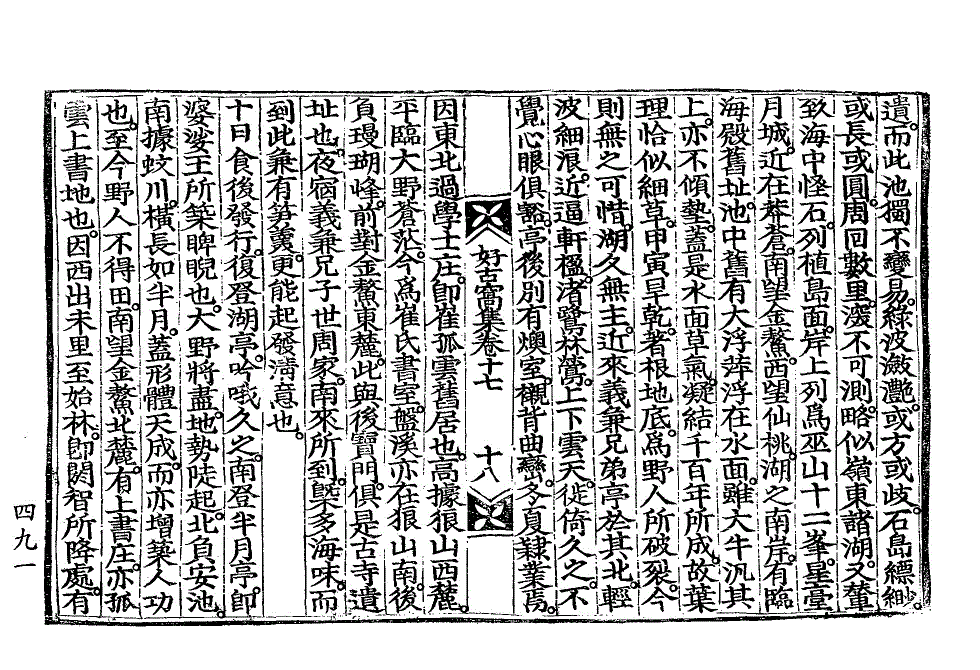 遗。而此池独不变易。绿波潋滟。或方或歧。石岛缥缈。或长或圆。周回数里。深不可测。略似岭东诸湖。又辇致海中怪石。列植岛面。岸上列为巫山十二峰。星台月城。近在莽苍。南望金鳌。西望仙桃。湖之南岸。有临海殿旧址。池中旧有大浮萍浮在水面。虽大牛汎其上。亦不倾垫。盖是水面草气。凝结千百年所成。故叶理恰似细草。甲寅旱乾。著根地底。为野人所破裂。今则无之可惜。湖久无主。近来义兼兄弟亭于其北。轻波细浪。近逼轩楹。渚鹭林莺。上下云天。徙倚久之。不觉心眼俱豁。亭后别有燠室。衬背曲峦。冬夏隶业焉。因东北过学士庄。即崔孤云旧居也。高据狼山西麓。平临大野苍茫。今为崔氏书室。盘溪亦在狼山南。后负㻴瑚峰。前对金鳌东麓。此与后宝门。俱是古寺遗址也。夜宿义兼兄子世周家。南来所到。槩多海味。而到此兼有笋羹。更能起发清意也。
遗。而此池独不变易。绿波潋滟。或方或歧。石岛缥缈。或长或圆。周回数里。深不可测。略似岭东诸湖。又辇致海中怪石。列植岛面。岸上列为巫山十二峰。星台月城。近在莽苍。南望金鳌。西望仙桃。湖之南岸。有临海殿旧址。池中旧有大浮萍浮在水面。虽大牛汎其上。亦不倾垫。盖是水面草气。凝结千百年所成。故叶理恰似细草。甲寅旱乾。著根地底。为野人所破裂。今则无之可惜。湖久无主。近来义兼兄弟亭于其北。轻波细浪。近逼轩楹。渚鹭林莺。上下云天。徙倚久之。不觉心眼俱豁。亭后别有燠室。衬背曲峦。冬夏隶业焉。因东北过学士庄。即崔孤云旧居也。高据狼山西麓。平临大野苍茫。今为崔氏书室。盘溪亦在狼山南。后负㻴瑚峰。前对金鳌东麓。此与后宝门。俱是古寺遗址也。夜宿义兼兄子世周家。南来所到。槩多海味。而到此兼有笋羹。更能起发清意也。十日食后发行。复登湖亭。吟哦久之。南登半月亭。即婆娑王所筑睥睨也。大野将尽。地势陡起。北负安池。南据蚊川。横长如半月。盖形体天成。而亦增筑人功也。至今野人不得田。南望金鳌北麓。有上书庄。亦孤云上书地也。因西出未里至始林。即阏智所降处。有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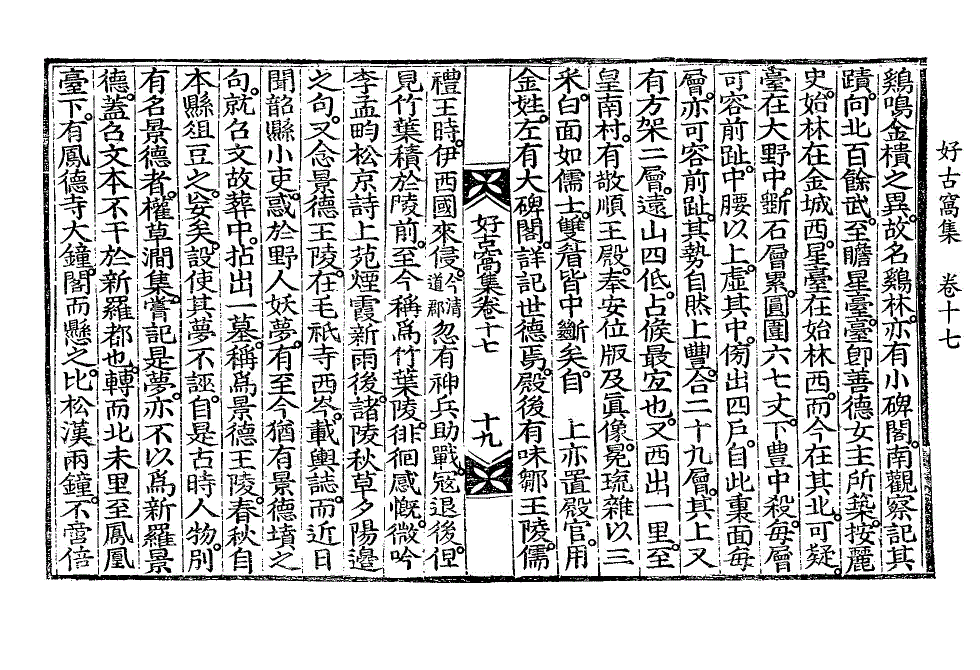 鸡鸣金樻之异。故名鸡林。亦有小碑阁。南观察记其迹。向北百馀武。至瞻星台。台即善德女主所筑。按丽史。始林在金城西。星台在始林西。而今在其北。可疑。台在大野中。斲石层累。圆围六七丈。下礼中杀。每层可容前趾。中腰以上。虚其中。傍出四户。自此里面每层。亦可容前趾。其势自然上丰。合二十九层。其上又有方架二层。远山四低。占候最宜也。又西出一里。至皇南村。有敬顺王殿。奉安位版及真像。冕琉杂以三采。白面如儒士。双眉皆中断矣。自 上亦置殿官。用金姓。左有大碑阁。详记世德焉。殿后有味邹王陵。儒礼王时。伊西国来侵。(今清道郡。)忽有神兵助战。寇退后。但见竹叶积于陵前。至今称为竹叶陵。徘徊感慨。微吟李孟畇松京诗上苑烟霞新雨后。诸陵秋草夕阳边之句。又念景德王陵。在毛祇寺西岑。载舆志。而近日闻韶县小吏。惑于野人妖梦。有至今犹有景德坟之句。就召文故葬中。拈出一墓。称为景德王陵。春秋自本县俎豆之。妄矣。设使其梦不诬。自是古时人物。别有名景德者。权草涧集。尝记是梦。亦不以为新罗景德。盖召文本不干于新罗都也。转而北未里至凤凰台下。有凤德寺大钟。阁而悬之。比松汉两钟。不啻倍
鸡鸣金樻之异。故名鸡林。亦有小碑阁。南观察记其迹。向北百馀武。至瞻星台。台即善德女主所筑。按丽史。始林在金城西。星台在始林西。而今在其北。可疑。台在大野中。斲石层累。圆围六七丈。下礼中杀。每层可容前趾。中腰以上。虚其中。傍出四户。自此里面每层。亦可容前趾。其势自然上丰。合二十九层。其上又有方架二层。远山四低。占候最宜也。又西出一里。至皇南村。有敬顺王殿。奉安位版及真像。冕琉杂以三采。白面如儒士。双眉皆中断矣。自 上亦置殿官。用金姓。左有大碑阁。详记世德焉。殿后有味邹王陵。儒礼王时。伊西国来侵。(今清道郡。)忽有神兵助战。寇退后。但见竹叶积于陵前。至今称为竹叶陵。徘徊感慨。微吟李孟畇松京诗上苑烟霞新雨后。诸陵秋草夕阳边之句。又念景德王陵。在毛祇寺西岑。载舆志。而近日闻韶县小吏。惑于野人妖梦。有至今犹有景德坟之句。就召文故葬中。拈出一墓。称为景德王陵。春秋自本县俎豆之。妄矣。设使其梦不诬。自是古时人物。别有名景德者。权草涧集。尝记是梦。亦不以为新罗景德。盖召文本不干于新罗都也。转而北未里至凤凰台下。有凤德寺大钟。阁而悬之。比松汉两钟。不啻倍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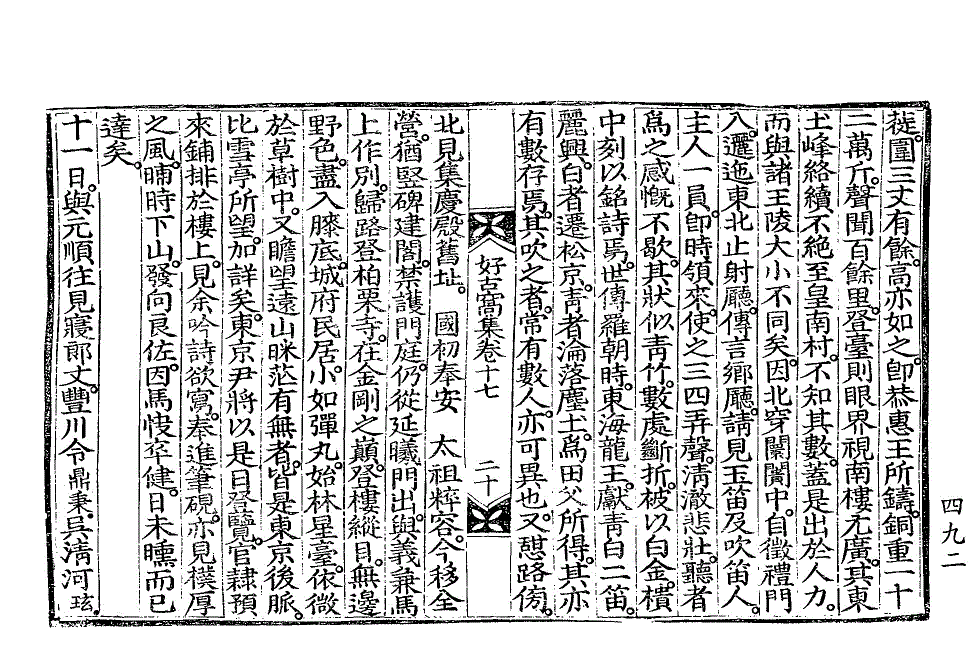 蓰。围三丈有馀。高亦如之。即恭惠王所铸。铜重一十二万斤。声闻百馀里。登台则眼界视南楼尤广。其东土峰络续不绝至皇南村。不知其数。盖是出于人力。而与诸王陵大小不同矣。因北穿阛阓中。自徵礼门入。逦迤东北止射厅。传言乡厅。请见玉笛及吹笛人。主人一员。即时领来。使之三四弄声。清澈悲壮。听者为之感慨不歇。其状似青竹。数处断折。被以白金。樻中刻以铭诗焉。世传罗朝时。东海龙王。献青白二笛。丽兴。白者迁松京。青者沦落尘土。为田父所得。其亦有数存焉。其吹之者。常有数人。亦可异也。又憩路傍。北见集庆殿旧址。 国初奉安 太祖粹容。今移全营。犹竖碑建阁。禁护门庭。仍从延曦门出。与义兼马上作别。归路登柏栗寺。在金刚之巅。登楼纵目。无边野色。尽入膝底。城府民居。小如弹丸。始林星台。依微于草树中。又瞻望远山
蓰。围三丈有馀。高亦如之。即恭惠王所铸。铜重一十二万斤。声闻百馀里。登台则眼界视南楼尤广。其东土峰络续不绝至皇南村。不知其数。盖是出于人力。而与诸王陵大小不同矣。因北穿阛阓中。自徵礼门入。逦迤东北止射厅。传言乡厅。请见玉笛及吹笛人。主人一员。即时领来。使之三四弄声。清澈悲壮。听者为之感慨不歇。其状似青竹。数处断折。被以白金。樻中刻以铭诗焉。世传罗朝时。东海龙王。献青白二笛。丽兴。白者迁松京。青者沦落尘土。为田父所得。其亦有数存焉。其吹之者。常有数人。亦可异也。又憩路傍。北见集庆殿旧址。 国初奉安 太祖粹容。今移全营。犹竖碑建阁。禁护门庭。仍从延曦门出。与义兼马上作别。归路登柏栗寺。在金刚之巅。登楼纵目。无边野色。尽入膝底。城府民居。小如弹丸。始林星台。依微于草树中。又瞻望远山十一日。与元顺往见寝郎丈。丰川令(鼎秉),吴清河(玹),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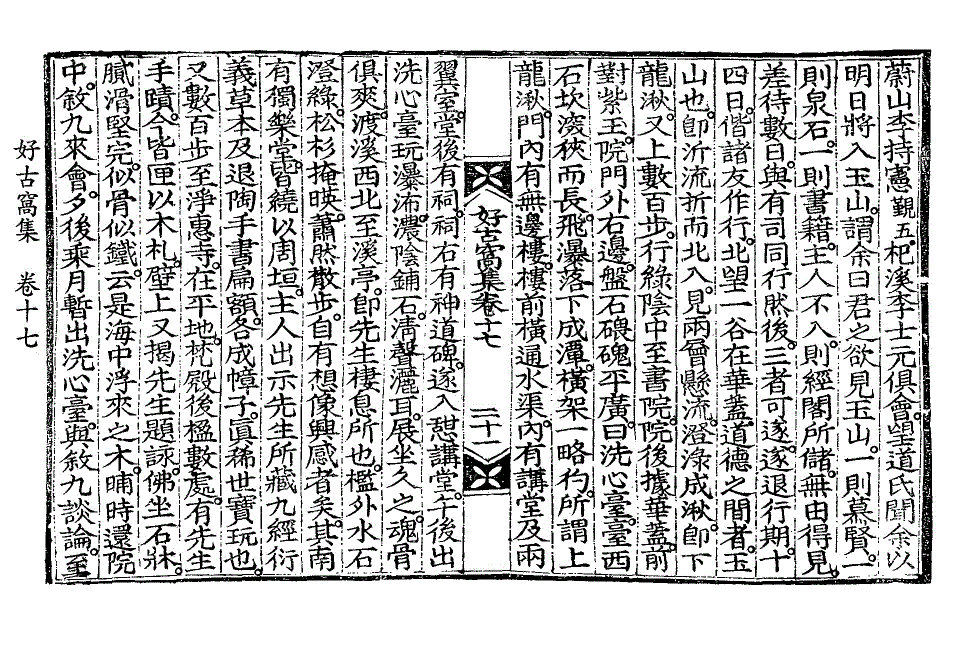 蔚山李持宪(觐五),杞溪李士元俱会。望道氏闻余以明日将入玉山。谓余曰君之欲见玉山。一则慕贤。一则泉石。一则书籍。主人不入。则经阁所储。无由得见。差待数日。与有司同行然后。三者可遂。遂退行期。十四日。偕诸友作行。北望一谷在华盖,道德之间者。玉山也。即沂流折而北入。见两层悬流。澄渌成湫。即下龙湫。又上数百步。行绿阴中至书院。院后据华盖。前对紫玉。院门外右边。盘石碨磈平广。曰洗心台。台西石坎深狭而长。飞瀑落下成潭。横架一略彴。所谓上龙湫。门内有无边楼。楼前横通水渠。内有讲堂及两翼室。堂后有祠。祠右有神道碑。遂入憩讲堂。午后出洗心台玩瀑㳍。浓阴铺石。清声洒耳。展坐久之。魂骨俱爽。渡溪西北至溪亭。即先生栖息所也。槛外水石澄绿。松杉掩映。萧然散步。自有想像兴感者矣。其南有独乐堂。皆绕以周垣。主人出示先生所藏九经衍义草本及退陶手书扁额。各成幛子。真稀世宝玩也。又数百步至净惠寺。在平地。梵殿后楹数处。有先生手迹。今皆匣以木札。壁上又揭先生题咏。佛坐石床。腻滑坚完。似骨似铁。云是海中浮来之木。晡时还院中。叙九来会。夕后乘月暂出洗心台。与叙九谈论。至
蔚山李持宪(觐五),杞溪李士元俱会。望道氏闻余以明日将入玉山。谓余曰君之欲见玉山。一则慕贤。一则泉石。一则书籍。主人不入。则经阁所储。无由得见。差待数日。与有司同行然后。三者可遂。遂退行期。十四日。偕诸友作行。北望一谷在华盖,道德之间者。玉山也。即沂流折而北入。见两层悬流。澄渌成湫。即下龙湫。又上数百步。行绿阴中至书院。院后据华盖。前对紫玉。院门外右边。盘石碨磈平广。曰洗心台。台西石坎深狭而长。飞瀑落下成潭。横架一略彴。所谓上龙湫。门内有无边楼。楼前横通水渠。内有讲堂及两翼室。堂后有祠。祠右有神道碑。遂入憩讲堂。午后出洗心台玩瀑㳍。浓阴铺石。清声洒耳。展坐久之。魂骨俱爽。渡溪西北至溪亭。即先生栖息所也。槛外水石澄绿。松杉掩映。萧然散步。自有想像兴感者矣。其南有独乐堂。皆绕以周垣。主人出示先生所藏九经衍义草本及退陶手书扁额。各成幛子。真稀世宝玩也。又数百步至净惠寺。在平地。梵殿后楹数处。有先生手迹。今皆匣以木札。壁上又揭先生题咏。佛坐石床。腻滑坚完。似骨似铁。云是海中浮来之木。晡时还院中。叙九来会。夕后乘月暂出洗心台。与叙九谈论。至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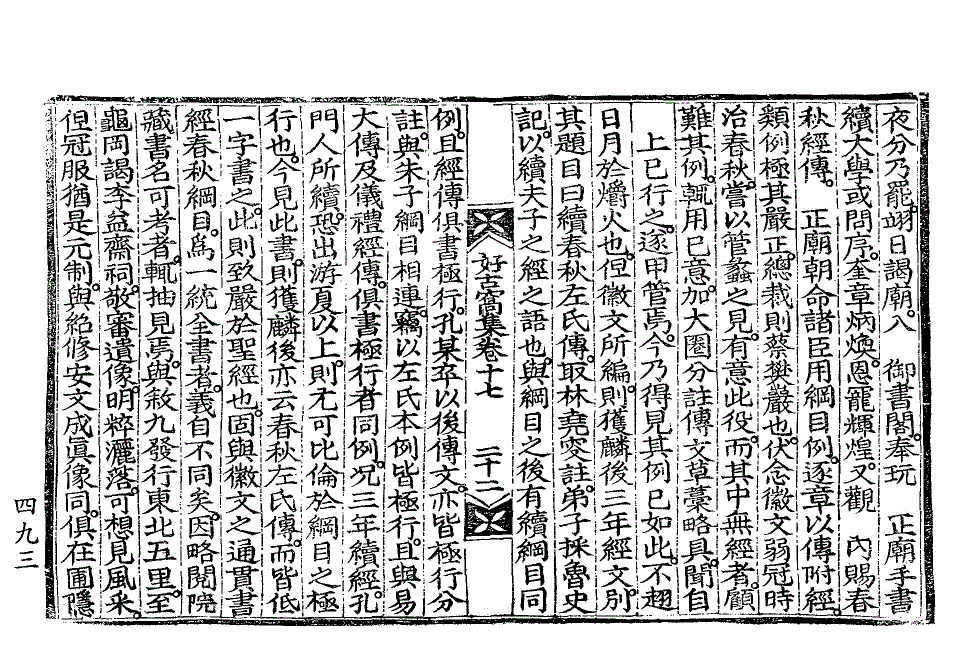 夜分乃罢。翊日谒庙。入 御书阁。奉玩 正庙手书续大学或问序。奎章炳焕。恩宠辉煌。又观 内赐春秋经传。 正庙朝命诸臣用纲目例。逐章以传附经。类例极其严正。总裁则蔡樊岩也。伏念徽文弱冠时治春秋。尝以管蠡之见。有意此役。而其中无经者。顾难其例。辄用己意。加大圈分注传文草藁略具。闻自 上已行之。遂甲管焉。今乃得见其例已如此。不趐日月于爝火也。但徽文所编。则获麟后三年经文。别其题目曰续春秋左氏传。取林尧叟注。弟子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之语也。与纲目之后有续纲目同例。且经传俱书极行。孔某卒以后传文。亦皆极行分注。与朱子纲目相连。窃以左氏本例皆极行。且与易大传及仪礼经传。俱书极行者同例。况三年续经。孔门人所续。恐出游夏以上。则尤可比伦于纲目之极行也。今见此书。则获麟后亦云春秋左氏传。而皆低一字书之。此则致严于圣经也。固与徽文之通贯书经春秋纲目。为一统全书者。义自不同矣。因略阅院藏书名可考者。辄抽见焉。与叙九发行东北五里。至龟冈谒李益斋祠。敬审遗像。明粹洒落。可想见风采。但冠服犹是元制。与绍修安文成真像同。俱在圃隐
夜分乃罢。翊日谒庙。入 御书阁。奉玩 正庙手书续大学或问序。奎章炳焕。恩宠辉煌。又观 内赐春秋经传。 正庙朝命诸臣用纲目例。逐章以传附经。类例极其严正。总裁则蔡樊岩也。伏念徽文弱冠时治春秋。尝以管蠡之见。有意此役。而其中无经者。顾难其例。辄用己意。加大圈分注传文草藁略具。闻自 上已行之。遂甲管焉。今乃得见其例已如此。不趐日月于爝火也。但徽文所编。则获麟后三年经文。别其题目曰续春秋左氏传。取林尧叟注。弟子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之语也。与纲目之后有续纲目同例。且经传俱书极行。孔某卒以后传文。亦皆极行分注。与朱子纲目相连。窃以左氏本例皆极行。且与易大传及仪礼经传。俱书极行者同例。况三年续经。孔门人所续。恐出游夏以上。则尤可比伦于纲目之极行也。今见此书。则获麟后亦云春秋左氏传。而皆低一字书之。此则致严于圣经也。固与徽文之通贯书经春秋纲目。为一统全书者。义自不同矣。因略阅院藏书名可考者。辄抽见焉。与叙九发行东北五里。至龟冈谒李益斋祠。敬审遗像。明粹洒落。可想见风采。但冠服犹是元制。与绍修安文成真像同。俱在圃隐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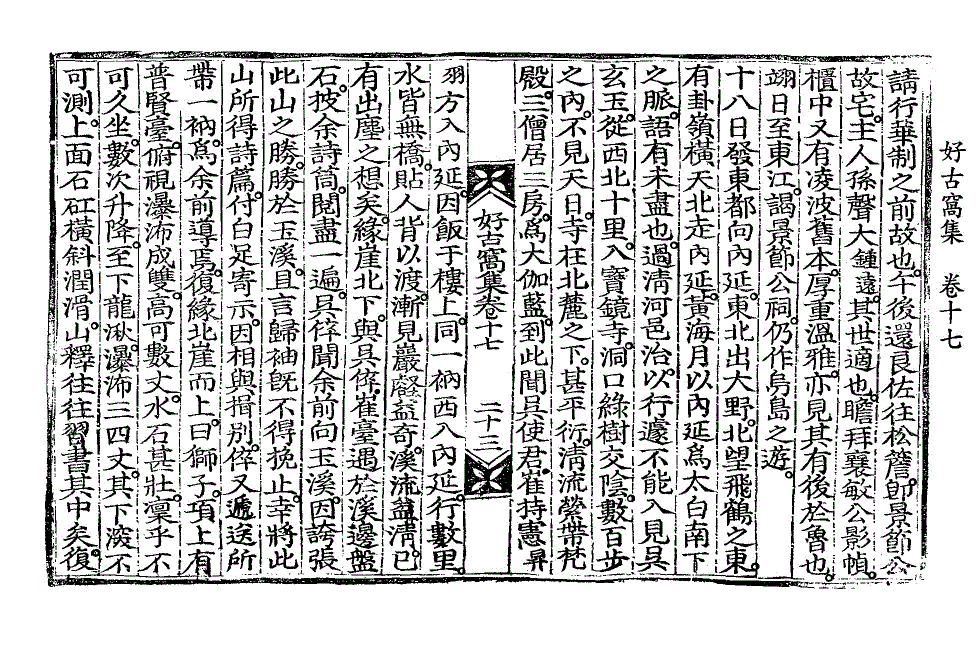 请行华制之前故也。午后还良佐往松檐。即景节公故宅。主人孙声大(钟远)。其世适也。瞻拜襄敏公影帧。匮中又有凌波旧本。厚重温雅。亦见其有后于鲁也。翊日至东江。谒景节公祠。仍作乌岛之游。
请行华制之前故也。午后还良佐往松檐。即景节公故宅。主人孙声大(钟远)。其世适也。瞻拜襄敏公影帧。匮中又有凌波旧本。厚重温雅。亦见其有后于鲁也。翊日至东江。谒景节公祠。仍作乌岛之游。十八日发东都向内延。东北出大野。北望飞鹤之东。有卦岭横天北走内延。黄海月以内延为太白南下之脉。语有未尽也。过清河邑治。以行遽不能入见吴玄玉。从西北十里。入宝镜寺。洞口绿树交阴。数百步之内。不见天日。寺在北麓之下。甚平衍。清流萦带梵殿。三僧居三房。为大伽蓝。到此闻吴使君,崔持宪(升羽)方入内延。因饭于楼上。同一衲西入内延。行数里。水皆无桥。贴人背以渡。渐见岩壑益奇。溪流益清。已有出尘之想矣。缘崖北下。与吴倅,崔台遇于溪边盘石。披余诗筒。阅尽一遍。吴倅闻余前向玉溪。因誇张此山之胜。胜于玉溪。且言归袖既不得挽止。幸将此山所得诗篇。付白足寄示。因相与揖别。倅又递送所带一衲。为余前导焉。复缘北崖而上。曰狮子。项上有普贤台。俯视瀑㳍成双。高可数丈。水石甚壮。凛乎不可久坐。数次升降。至下龙湫。瀑㳍三四丈。其下深不可测。上面石矼横斜润滑。山释往往习书其中矣。复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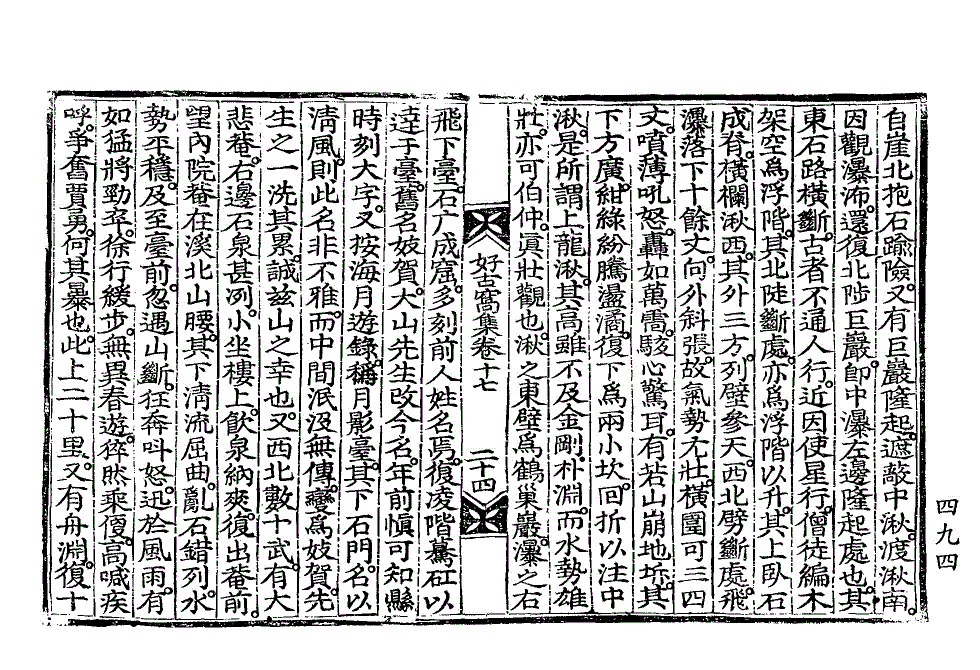 自崖北抱石踰险。又有巨岩隆起。遮蔽中湫。渡湫南。因观瀑㳍。还复北陟巨岩。即中瀑左边隆起处也。其东石路横断。古者不通人行。近因使星行。僧徒编木架空为浮阶。其北陡断处。亦为浮阶以升。其上卧石成脊。横栏湫西。其外三方。列壁参天。西北劈断处。飞瀑落下十馀丈。向外斜张。故气势尤壮。横围可三四丈。喷薄吼怒。轰如万䨓。骇心惊耳。有若山崩地坼。其下方广。绀绿纷腾荡潏。复下为两小坎。回折以注中湫。是所谓上龙湫。其高虽不及金刚,朴渊。而水势雄壮。亦可伯仲。真壮观也。湫之东壁为鹤巢岩。瀑之右飞下台。石广成窟。多刻前人姓名焉。复凌阶蓦矼以达于台。旧名妓贺。大山先生改今名。年前慎可知县时刻大字。又按海月游录。称月影台。其下石门。名以清风。则此名非不雅。而中间泯没无传。变为妓贺。先生之一洗其累。诚玆山之幸也。又西北数十武。有大悲庵。右边石泉甚冽。小坐楼上。饮泉纳爽。复出庵前。望内院庵在溪北山腰。其下清流屈曲。乱石错列。水势平稳。及至台前。忽遇山断。狂奔叫怒。迅于风雨。有如猛将劲卒。徐行缓步。无异春游。猝然乘便。高喊疾呼。争奋贾勇。何其㬥也。此上二十里。又有舟渊。复十
自崖北抱石踰险。又有巨岩隆起。遮蔽中湫。渡湫南。因观瀑㳍。还复北陟巨岩。即中瀑左边隆起处也。其东石路横断。古者不通人行。近因使星行。僧徒编木架空为浮阶。其北陡断处。亦为浮阶以升。其上卧石成脊。横栏湫西。其外三方。列壁参天。西北劈断处。飞瀑落下十馀丈。向外斜张。故气势尤壮。横围可三四丈。喷薄吼怒。轰如万䨓。骇心惊耳。有若山崩地坼。其下方广。绀绿纷腾荡潏。复下为两小坎。回折以注中湫。是所谓上龙湫。其高虽不及金刚,朴渊。而水势雄壮。亦可伯仲。真壮观也。湫之东壁为鹤巢岩。瀑之右飞下台。石广成窟。多刻前人姓名焉。复凌阶蓦矼以达于台。旧名妓贺。大山先生改今名。年前慎可知县时刻大字。又按海月游录。称月影台。其下石门。名以清风。则此名非不雅。而中间泯没无传。变为妓贺。先生之一洗其累。诚玆山之幸也。又西北数十武。有大悲庵。右边石泉甚冽。小坐楼上。饮泉纳爽。复出庵前。望内院庵在溪北山腰。其下清流屈曲。乱石错列。水势平稳。及至台前。忽遇山断。狂奔叫怒。迅于风雨。有如猛将劲卒。徐行缓步。无异春游。猝然乘便。高喊疾呼。争奋贾勇。何其㬥也。此上二十里。又有舟渊。复十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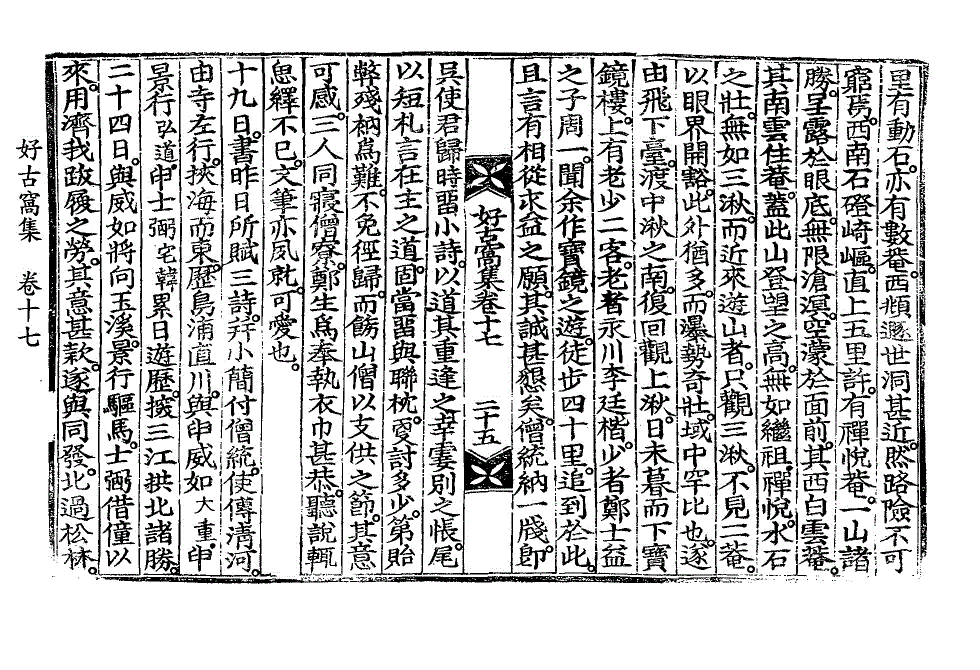 里有动石。亦有数庵。西頫遁世洞甚近。然路险不可穷焉。西南石磴崎岖。直上五里许。有禅悦庵。一山诸胜。呈露于眼底。无限沧溟。空濛于面前。其西白云庵。其南云住庵。盖此山登望之高。无如继祖,禅悦。水石之壮。无如三湫。而近来游山者。只观三湫。不见二庵。以眼界开豁。此外犹多。而瀑势奇壮。域中罕比也。遂由飞下台。渡中湫之南。复回观上湫。日未暮而下宝镜楼。上有老少二客。老者永川李廷楷。少者郑士益之子周一。闻余作宝镜之游。徒步四十里。追到于此。且言有相从求益之愿。其诚甚恳矣。僧统纳一笺。即吴使君归时留小诗。以道其重逢之幸霎别之怅。尾以短札言在主之道。固当留与联枕。更讨多少。第贻弊残衲为难。不免径归。而饬山僧以支供之节。其意可感。三人同寝僧寮。郑生为奉执衣巾甚恭。听说辄思绎不已。文笔亦夙就。可爱也。
里有动石。亦有数庵。西頫遁世洞甚近。然路险不可穷焉。西南石磴崎岖。直上五里许。有禅悦庵。一山诸胜。呈露于眼底。无限沧溟。空濛于面前。其西白云庵。其南云住庵。盖此山登望之高。无如继祖,禅悦。水石之壮。无如三湫。而近来游山者。只观三湫。不见二庵。以眼界开豁。此外犹多。而瀑势奇壮。域中罕比也。遂由飞下台。渡中湫之南。复回观上湫。日未暮而下宝镜楼。上有老少二客。老者永川李廷楷。少者郑士益之子周一。闻余作宝镜之游。徒步四十里。追到于此。且言有相从求益之愿。其诚甚恳矣。僧统纳一笺。即吴使君归时留小诗。以道其重逢之幸霎别之怅。尾以短札言在主之道。固当留与联枕。更讨多少。第贻弊残衲为难。不免径归。而饬山僧以支供之节。其意可感。三人同寝僧寮。郑生为奉执衣巾甚恭。听说辄思绎不已。文笔亦夙就。可爱也。十九日。书昨日所赋三诗。并小简付僧统。使传清河。由寺左行。挟海而东。历鸟浦直川。与申威如(大重),申景行(弘道),申士弼(宅韩)累日游历。探三江拱北诸胜。
二十四日。与威如将向玉溪。景行驱马。士弼借僮以来。用济我跋履之劳。其意甚款。遂与同发。北过松林。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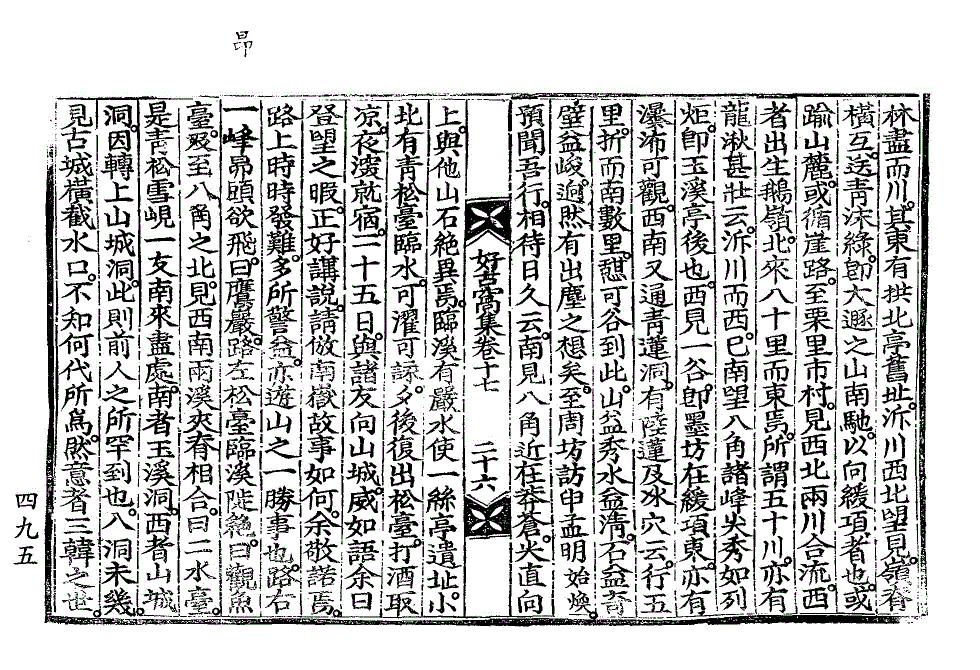 林尽而川。其东有拱北亭旧址。溯川西北望见。岭脊横互。送青沫绿。即大遁之山南驰。以向缓项者也。或踰山麓。或循崖路。至栗里市村。见西北两川合流。西者出生鹅岭。北来八十里而东焉。所谓五十川。亦有龙湫甚壮云。溯川而西。已南望八角诸峰尖秀如列炬。即玉溪亭后也。西见一谷。即墨坊在缓项东。亦有瀑㳍可观。西南又通青莲洞。有陆莲及冰穴云。行五里。折而南数里。憩可谷到此。山益秀水益清。石益奇壁益峻。迥然有出尘之想矣。至周坊访申孟明(始焕)。预闻吾行。相待日久云。南见八角近在莽苍。尖直向上。与他山石绝异焉。临溪有严水使一丝亭遗址。小北有青松台临水。可濯可咏。夕后复出松台。打酒取凉。夜深就宿。二十五日。与诸友向山城。威如语余曰登望之暇。正好讲说。请仿南岳故事如何。余敬诺焉。路上时时发难。多所警益。亦游山之一胜事也。路右一峰昴(一作昂)头欲飞。曰鹰岩。路左松台临溪𨺗绝。曰观鱼台。及至八角之北。见西南两溪夹脊相合。曰二水台。是青松雪岘一支南来尽处。南者玉溪洞。西者山城洞。因转上山城洞。此则前人之所罕到也。入洞未几。见古城横截水口。不知何代所为。然意者三韩之世。
林尽而川。其东有拱北亭旧址。溯川西北望见。岭脊横互。送青沫绿。即大遁之山南驰。以向缓项者也。或踰山麓。或循崖路。至栗里市村。见西北两川合流。西者出生鹅岭。北来八十里而东焉。所谓五十川。亦有龙湫甚壮云。溯川而西。已南望八角诸峰尖秀如列炬。即玉溪亭后也。西见一谷。即墨坊在缓项东。亦有瀑㳍可观。西南又通青莲洞。有陆莲及冰穴云。行五里。折而南数里。憩可谷到此。山益秀水益清。石益奇壁益峻。迥然有出尘之想矣。至周坊访申孟明(始焕)。预闻吾行。相待日久云。南见八角近在莽苍。尖直向上。与他山石绝异焉。临溪有严水使一丝亭遗址。小北有青松台临水。可濯可咏。夕后复出松台。打酒取凉。夜深就宿。二十五日。与诸友向山城。威如语余曰登望之暇。正好讲说。请仿南岳故事如何。余敬诺焉。路上时时发难。多所警益。亦游山之一胜事也。路右一峰昴(一作昂)头欲飞。曰鹰岩。路左松台临溪𨺗绝。曰观鱼台。及至八角之北。见西南两溪夹脊相合。曰二水台。是青松雪岘一支南来尽处。南者玉溪洞。西者山城洞。因转上山城洞。此则前人之所罕到也。入洞未几。见古城横截水口。不知何代所为。然意者三韩之世。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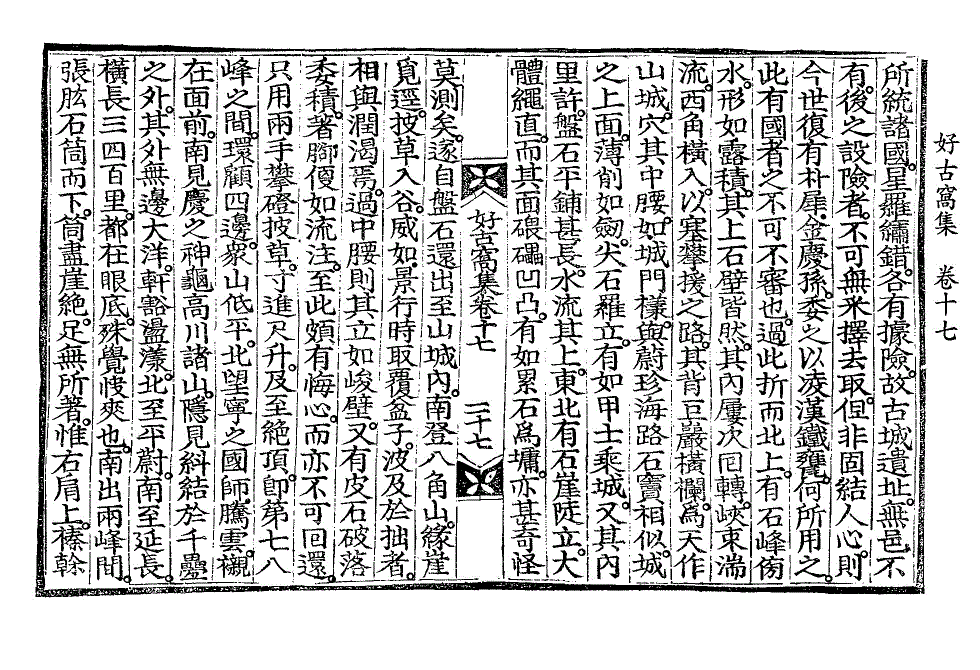 所统诸国。星罗绣错。各有据险。故古城遗址。无邑不有。后之设险者。不可无采择去取。但非固结人心。则今世复有朴犀,金庆孙。委之以凌汉铁瓮。何所用之。此有国者之不可不审也。过此折而北上。有石峰傍水。形如露积。其上石壁皆然。其内屡次回转。峡束湍流。西角横入。以塞攀援之路。其背巨岩横栏。为天作山城。穴其中腰。如城门样。与蔚珍海路石窦相似。城之上面。薄削如剑。尖石罗立。有如甲士乘城。又其内里许。盘石平铺甚长。水流其上。东北有石崖陡立。大体绳直。而其面碨礧凹凸。有如累石为墉。亦甚奇怪莫测矣。遂自盘石还出至山城内。南登八角山。缘崖觅径。披草入谷。威如,景行时取覆盆子。波及于拙者。相与润渴焉。过中腰则其立如峻壁。又有皮石破落委积。著脚便如流注。至此颇有悔心。而亦不可回还。只用两手攀磴披草。寸进尺升。及至绝顶。即第七八峰之间。环顾四边。众山低平。北望宁之国师,腾云。衬在面前。南见庆之神龟高川诸山。隐见纠结于千叠之外。其外无边大洋。轩豁荡漾。北至平蔚。南至延长。横长三四百里。都在眼底。殊觉快爽也。南出两峰间。张肱石筒而下。筒尽崖绝。足无所著。惟右肩上。榛干
所统诸国。星罗绣错。各有据险。故古城遗址。无邑不有。后之设险者。不可无采择去取。但非固结人心。则今世复有朴犀,金庆孙。委之以凌汉铁瓮。何所用之。此有国者之不可不审也。过此折而北上。有石峰傍水。形如露积。其上石壁皆然。其内屡次回转。峡束湍流。西角横入。以塞攀援之路。其背巨岩横栏。为天作山城。穴其中腰。如城门样。与蔚珍海路石窦相似。城之上面。薄削如剑。尖石罗立。有如甲士乘城。又其内里许。盘石平铺甚长。水流其上。东北有石崖陡立。大体绳直。而其面碨礧凹凸。有如累石为墉。亦甚奇怪莫测矣。遂自盘石还出至山城内。南登八角山。缘崖觅径。披草入谷。威如,景行时取覆盆子。波及于拙者。相与润渴焉。过中腰则其立如峻壁。又有皮石破落委积。著脚便如流注。至此颇有悔心。而亦不可回还。只用两手攀磴披草。寸进尺升。及至绝顶。即第七八峰之间。环顾四边。众山低平。北望宁之国师,腾云。衬在面前。南见庆之神龟高川诸山。隐见纠结于千叠之外。其外无边大洋。轩豁荡漾。北至平蔚。南至延长。横长三四百里。都在眼底。殊觉快爽也。南出两峰间。张肱石筒而下。筒尽崖绝。足无所著。惟右肩上。榛干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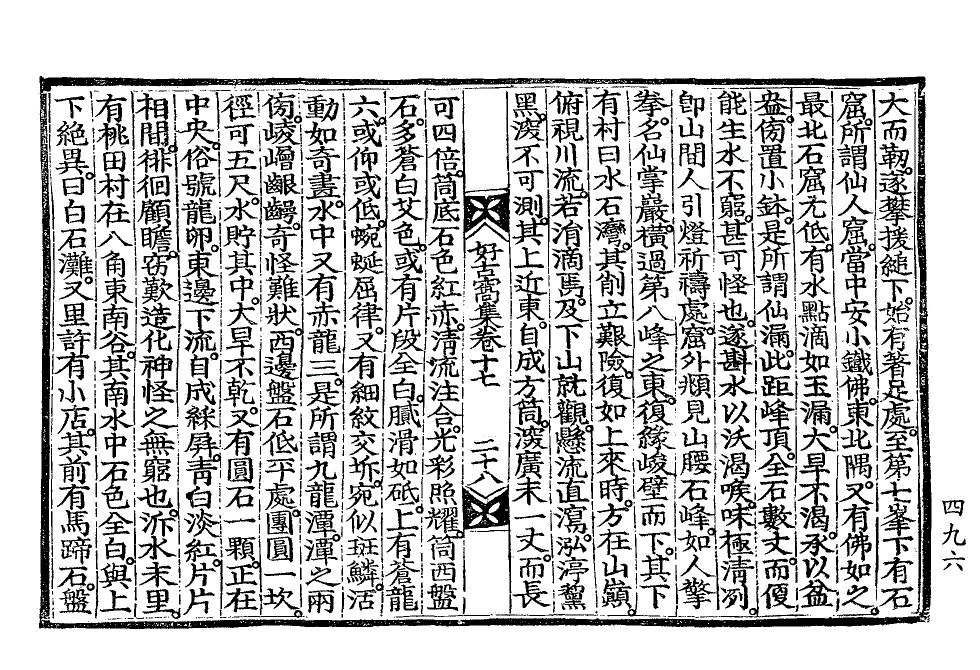 大而韧。遂攀援缒下。始有著足处。至第七峰下有石窟。所谓仙人窟。当中安小铁佛。东北隅。又有佛如之。最北石窟尤低。有水点滴如玉漏。大旱不渴。承以盆盎。傍置小钵。是所谓仙漏。此距峰顶。全石数丈。而便能生水不穷。甚可怪也。遂斟水以沃渴喉。味极清冽。即山间人引灯祈祷处。窟外頫见山腰石峰。如人擎拳。名仙掌岩。横过第八峰之东。复缘峻壁而下。其下有村曰水石湾。其削立艰险。复如上来时。方在山巅。俯视川流。若涓滴焉。及下山就观。悬流直泻。泓渟黧黑。深不可测。其上近东。自成方筒。深广未一丈。而长可四倍。筒底石色红赤。清流注合。光彩照耀。筒西盘石。多苍白艾色。或有片段全白。腻滑如砥。上有苍龙六。或仰或低。蜿蜒屈律。又有细纹交坼。宛似斑鳞。活动如奇画。水中又有赤龙三。是所谓九龙潭。潭之两傍。崚嶒龈腭。奇怪难状。西边盘石低平处。团圆一坎。径可五尺。水贮其中。大旱不乾。又有圆石一颗。正在中央。俗号龙卵。东边下流。自成䌽屏。青白淡红。片片相间。徘徊顾瞻。窃叹造化神怪之无穷也。溯水未里。有桃田村在八角东南谷。其南水中石色全白。与上下绝异。曰白石滩。又里许有小店。其前有马蹄石。盘
大而韧。遂攀援缒下。始有著足处。至第七峰下有石窟。所谓仙人窟。当中安小铁佛。东北隅。又有佛如之。最北石窟尤低。有水点滴如玉漏。大旱不渴。承以盆盎。傍置小钵。是所谓仙漏。此距峰顶。全石数丈。而便能生水不穷。甚可怪也。遂斟水以沃渴喉。味极清冽。即山间人引灯祈祷处。窟外頫见山腰石峰。如人擎拳。名仙掌岩。横过第八峰之东。复缘峻壁而下。其下有村曰水石湾。其削立艰险。复如上来时。方在山巅。俯视川流。若涓滴焉。及下山就观。悬流直泻。泓渟黧黑。深不可测。其上近东。自成方筒。深广未一丈。而长可四倍。筒底石色红赤。清流注合。光彩照耀。筒西盘石。多苍白艾色。或有片段全白。腻滑如砥。上有苍龙六。或仰或低。蜿蜒屈律。又有细纹交坼。宛似斑鳞。活动如奇画。水中又有赤龙三。是所谓九龙潭。潭之两傍。崚嶒龈腭。奇怪难状。西边盘石低平处。团圆一坎。径可五尺。水贮其中。大旱不乾。又有圆石一颗。正在中央。俗号龙卵。东边下流。自成䌽屏。青白淡红。片片相间。徘徊顾瞻。窃叹造化神怪之无穷也。溯水未里。有桃田村在八角东南谷。其南水中石色全白。与上下绝异。曰白石滩。又里许有小店。其前有马蹄石。盘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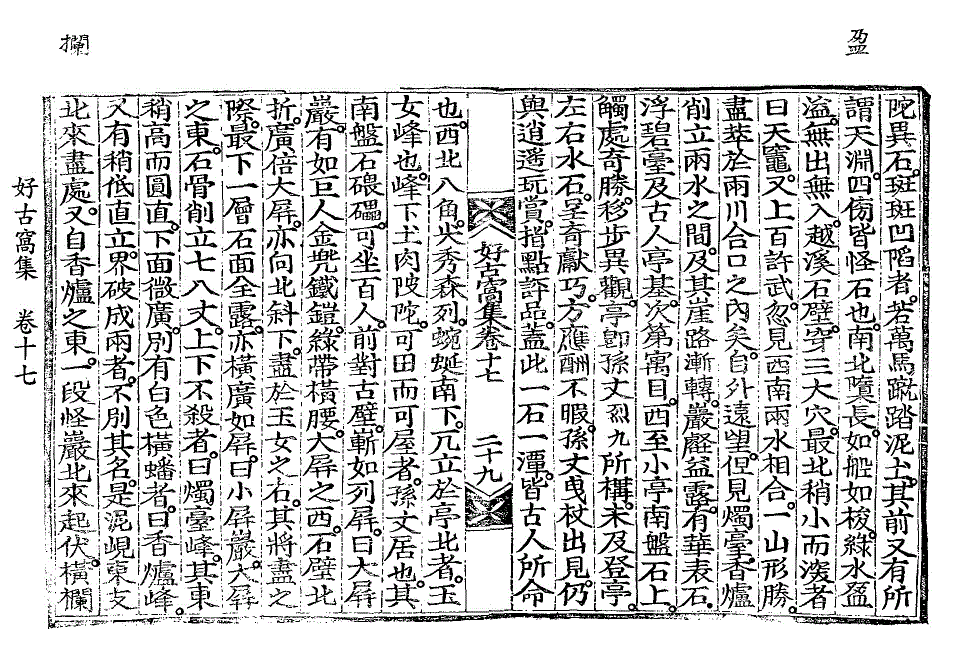 陀异石。斑斑凹陷者。若万马蹴踏泥土。其前又有所谓天渊。四傍皆怪石也。南北㯐长。如船如梭。绿水盈溢。无出无入。越溪石壁。穿三大穴。最北稍小而深者曰天灶。又上百许武。忽见西南两水相合。一山形胜。尽萃于两川合口之内矣。自外远望。但见烛台,香炉削立两水之间。及其崖路渐转。岩壑益露。有华表石,浮碧台及古人亭基。次第寓目。西至小亭南盘石上。触处奇胜。移步异观。亭即孙丈(烈九)所构。未及登亭。左右水石。呈奇献巧。方应酬不暇。孙丈曳杖出见。仍与逍遥玩赏。指点评品。盖此一石一潭。皆古人所命也。西北八角。尖秀森列。蜿蜒南下。兀立于亭北者。玉女峰也。峰下土肉陂陀。可田而可屋者。孙丈居也。其南盘石碨礧。可坐百人。前对古壁。崭如列屏。曰大屏岩。有如巨人金兜铁铠。绿带横腰。大屏之西。石壁北折。广倍大屏。亦向北斜下。尽于玉女之右。其将尽之际。最下一层石面全露。亦横广如屏。曰小屏岩。大屏之东。石骨削立七八丈。上下不杀者。曰烛台峰。其东稍高而圆直。下面微广。别有白色横蟠者。曰香炉峰。又有稍低直立。界破成两者。不别其名。是泥岘东支北来尽处。又自香炉之东。一段怪岩北来起伏。横栏(一作拦)
陀异石。斑斑凹陷者。若万马蹴踏泥土。其前又有所谓天渊。四傍皆怪石也。南北㯐长。如船如梭。绿水盈溢。无出无入。越溪石壁。穿三大穴。最北稍小而深者曰天灶。又上百许武。忽见西南两水相合。一山形胜。尽萃于两川合口之内矣。自外远望。但见烛台,香炉削立两水之间。及其崖路渐转。岩壑益露。有华表石,浮碧台及古人亭基。次第寓目。西至小亭南盘石上。触处奇胜。移步异观。亭即孙丈(烈九)所构。未及登亭。左右水石。呈奇献巧。方应酬不暇。孙丈曳杖出见。仍与逍遥玩赏。指点评品。盖此一石一潭。皆古人所命也。西北八角。尖秀森列。蜿蜒南下。兀立于亭北者。玉女峰也。峰下土肉陂陀。可田而可屋者。孙丈居也。其南盘石碨礧。可坐百人。前对古壁。崭如列屏。曰大屏岩。有如巨人金兜铁铠。绿带横腰。大屏之西。石壁北折。广倍大屏。亦向北斜下。尽于玉女之右。其将尽之际。最下一层石面全露。亦横广如屏。曰小屏岩。大屏之东。石骨削立七八丈。上下不杀者。曰烛台峰。其东稍高而圆直。下面微广。别有白色横蟠者。曰香炉峰。又有稍低直立。界破成两者。不别其名。是泥岘东支北来尽处。又自香炉之东。一段怪岩北来起伏。横栏(一作拦)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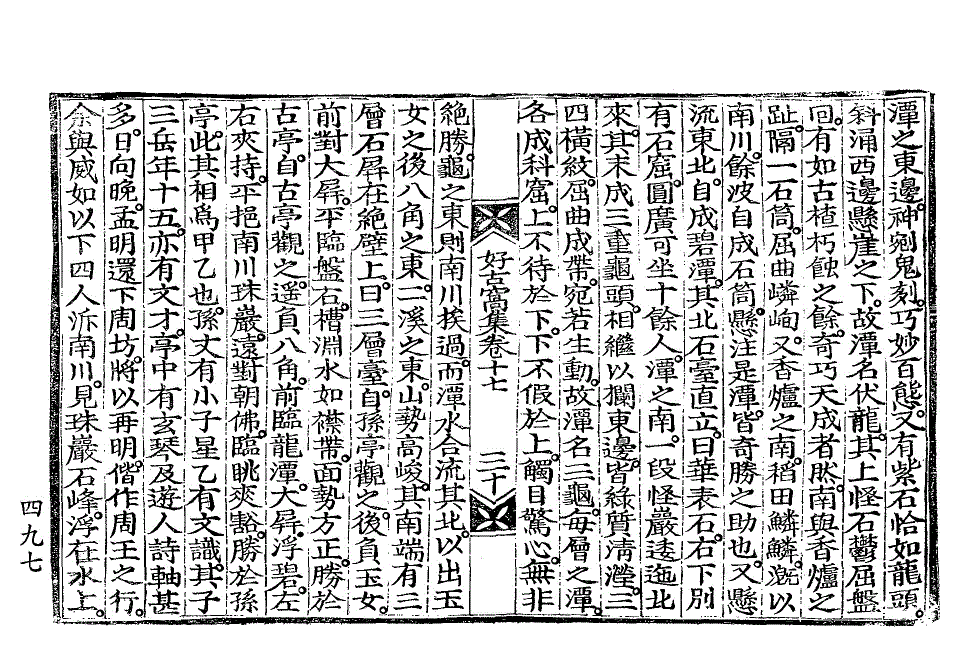 潭之东边。神剜鬼刻。巧妙百态。又有紫石恰如龙头。斜涌西边悬崖之下。故潭名伏龙。其上怪石郁屈盘回。有如古楂朽蚀之馀。奇巧天成者然。南与香炉之趾。隔一石筒。屈曲嶙峋。又香炉之南。稻田鳞鳞。溉以南川。馀波自成石筒。悬注是潭。皆奇胜之助也。又悬流东北。自成碧潭。其北石台直立。曰华表石。右下别有石窟。圆广可坐十馀人。潭之南。一段怪岩逶迤北来。其末成三重龟头。相继以拦东边。皆绿质清滢。三四横纹。屈曲成带。宛若生动。故潭名三龟。每层之潭。各成科窟。上不待于下。下不假于上。触目惊心。无非绝胜。龟之东则南川挨过。而潭水合流其北。以出玉女之后八角之东。二溪之东。山势高峻。其南端有三层石屏在绝壁上。曰三层台。自孙亭观之。后负玉女。前对大屏。平临盘石。槽渊水如襟带。面势方正。胜于古亭。自古亭观之。遥负八角。前临龙潭。大屏,浮碧。左右夹持。平挹南川珠岩。远对朝佛。临眺爽豁。胜于孙亭。此其相为甲乙也。孙丈有小子星乙有文识。其子三岳年十五。亦有文才。亭中有玄琴及游人诗轴甚多。日向晚。孟明还下周坊。将以再明。偕作周王之行。余与威如以下四人溯南川。见珠岩石峰。浮在水上。
潭之东边。神剜鬼刻。巧妙百态。又有紫石恰如龙头。斜涌西边悬崖之下。故潭名伏龙。其上怪石郁屈盘回。有如古楂朽蚀之馀。奇巧天成者然。南与香炉之趾。隔一石筒。屈曲嶙峋。又香炉之南。稻田鳞鳞。溉以南川。馀波自成石筒。悬注是潭。皆奇胜之助也。又悬流东北。自成碧潭。其北石台直立。曰华表石。右下别有石窟。圆广可坐十馀人。潭之南。一段怪岩逶迤北来。其末成三重龟头。相继以拦东边。皆绿质清滢。三四横纹。屈曲成带。宛若生动。故潭名三龟。每层之潭。各成科窟。上不待于下。下不假于上。触目惊心。无非绝胜。龟之东则南川挨过。而潭水合流其北。以出玉女之后八角之东。二溪之东。山势高峻。其南端有三层石屏在绝壁上。曰三层台。自孙亭观之。后负玉女。前对大屏。平临盘石。槽渊水如襟带。面势方正。胜于古亭。自古亭观之。遥负八角。前临龙潭。大屏,浮碧。左右夹持。平挹南川珠岩。远对朝佛。临眺爽豁。胜于孙亭。此其相为甲乙也。孙丈有小子星乙有文识。其子三岳年十五。亦有文才。亭中有玄琴及游人诗轴甚多。日向晚。孟明还下周坊。将以再明。偕作周王之行。余与威如以下四人溯南川。见珠岩石峰。浮在水上。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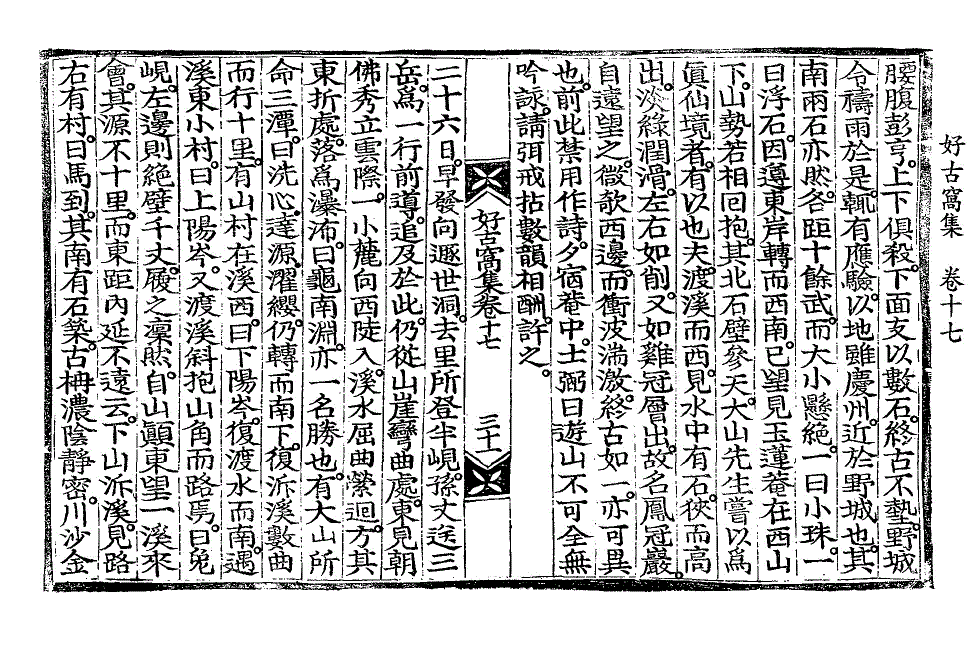 腰腹彭亨。上下俱杀。下面支以数石。终古不垫。野城令祷雨于是。辄有应验。以地虽庆州。近于野城也。其南两石亦然。各距十馀武。而大小悬绝。一曰小珠。一曰浮石。因遵东岸转而西南。已望见玉莲庵在西山下。山势若相回抱。其北石壁参天。大山先生尝以为真仙境者。有以也夫。渡溪而西。见水中有石。狭而高出。淡绿润滑。左右如削。又如鸡冠层出。故名凤冠岩。自远望之。微欹西边。而冲波湍激。终古如一。亦可异也。前此禁用作诗。夕宿庵中。士弼曰游山不可全无吟咏。请弭戒拈数韵相酬。许之。
腰腹彭亨。上下俱杀。下面支以数石。终古不垫。野城令祷雨于是。辄有应验。以地虽庆州。近于野城也。其南两石亦然。各距十馀武。而大小悬绝。一曰小珠。一曰浮石。因遵东岸转而西南。已望见玉莲庵在西山下。山势若相回抱。其北石壁参天。大山先生尝以为真仙境者。有以也夫。渡溪而西。见水中有石。狭而高出。淡绿润滑。左右如削。又如鸡冠层出。故名凤冠岩。自远望之。微欹西边。而冲波湍激。终古如一。亦可异也。前此禁用作诗。夕宿庵中。士弼曰游山不可全无吟咏。请弭戒拈数韵相酬。许之。二十六日。早发向遁世洞。去里所登半岘。孙丈送三岳。为一行前导。追及于此。仍从山崖弯曲处。东见朝佛秀立云际。一小麓向西陡入。溪水屈曲萦回。方其东折处。落为瀑㳍。曰龟南渊。亦一名胜也。有大山所命三潭。曰洗心,达源,濯缨。仍转而南下。复溯溪数曲而行十里。有山村在溪西。曰下阳岑。复渡水而南。遇溪东小村。曰上阳岑。又渡溪斜抱山角而路焉。曰兔岘。左边则绝壁千丈。履之凛然。自山颠东望一溪来会。其源不十里。而东距内延不远云。下山溯溪。见路右有村。曰马到。其南有石筑。古楠浓阴静密。川沙金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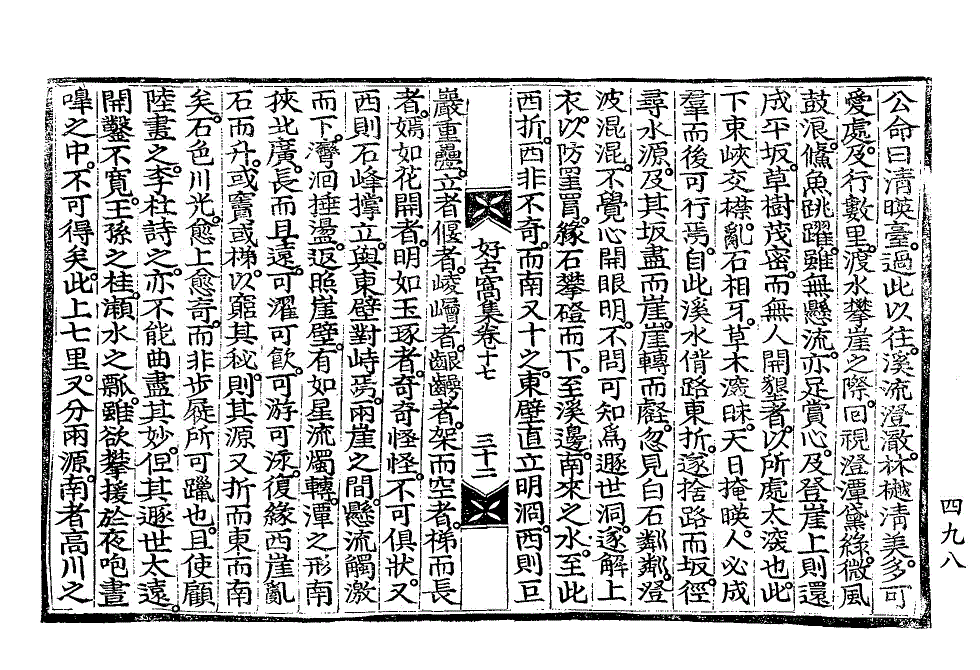 公命曰清映台。过此以往。溪流澄澈。林樾清美。多可爱处。及行数里。渡水攀崖之际。回视澄潭黛绿。微风鼓浪。鯈鱼跳跃。虽无悬流。亦足赏心。及登崖上则还成平坂。草树茂密。而无人开垦者。以所处太深也。此下束峡交襟。乱石相牙。草木深昧。天日掩映。人必成群而后可行焉。自此溪水背路东折。遂舍路而坂。径寻水源。及其坂尽而崖。崖转而壑。忽见白石粼粼。澄波混混。不觉心开眼明。不问可知为遁世洞。遂解上衣。以防挂罥。缘石攀磴而下。至溪边。南来之水。至此西折。西非不奇。而南又十之。东壁直立明浻。西则巨岩重叠。立者偃者。崚嶒者。龈腭者。架而空者。梯而长者。嫣如花开者。明如玉琢者。奇奇怪怪。不可俱状。又西则石峰撑立。与东壁对峙焉。两崖之间。悬流触激而下。湾洄捶荡。返照崖壁。有如星流烛转。潭之形南狭北广。长而且远。可濯可饮。可游可泳。复缘西崖乱石而升。或窦或梯。以穷其秘。则其源又折而东而南矣。石色川光。愈上愈奇。而非步屣所可躐也。且使顾陆画之。李杜诗之。亦不能曲尽其妙。但其遁世太远。开凿不宽。王孙之桂。𤃡水之瓢。虽欲攀援于夜咆昼嗥之中。不可得矣。此上七里。又分两源。南者高川之
公命曰清映台。过此以往。溪流澄澈。林樾清美。多可爱处。及行数里。渡水攀崖之际。回视澄潭黛绿。微风鼓浪。鯈鱼跳跃。虽无悬流。亦足赏心。及登崖上则还成平坂。草树茂密。而无人开垦者。以所处太深也。此下束峡交襟。乱石相牙。草木深昧。天日掩映。人必成群而后可行焉。自此溪水背路东折。遂舍路而坂。径寻水源。及其坂尽而崖。崖转而壑。忽见白石粼粼。澄波混混。不觉心开眼明。不问可知为遁世洞。遂解上衣。以防挂罥。缘石攀磴而下。至溪边。南来之水。至此西折。西非不奇。而南又十之。东壁直立明浻。西则巨岩重叠。立者偃者。崚嶒者。龈腭者。架而空者。梯而长者。嫣如花开者。明如玉琢者。奇奇怪怪。不可俱状。又西则石峰撑立。与东壁对峙焉。两崖之间。悬流触激而下。湾洄捶荡。返照崖壁。有如星流烛转。潭之形南狭北广。长而且远。可濯可饮。可游可泳。复缘西崖乱石而升。或窦或梯。以穷其秘。则其源又折而东而南矣。石色川光。愈上愈奇。而非步屣所可躐也。且使顾陆画之。李杜诗之。亦不能曲尽其妙。但其遁世太远。开凿不宽。王孙之桂。𤃡水之瓢。虽欲攀援于夜咆昼嗥之中。不可得矣。此上七里。又分两源。南者高川之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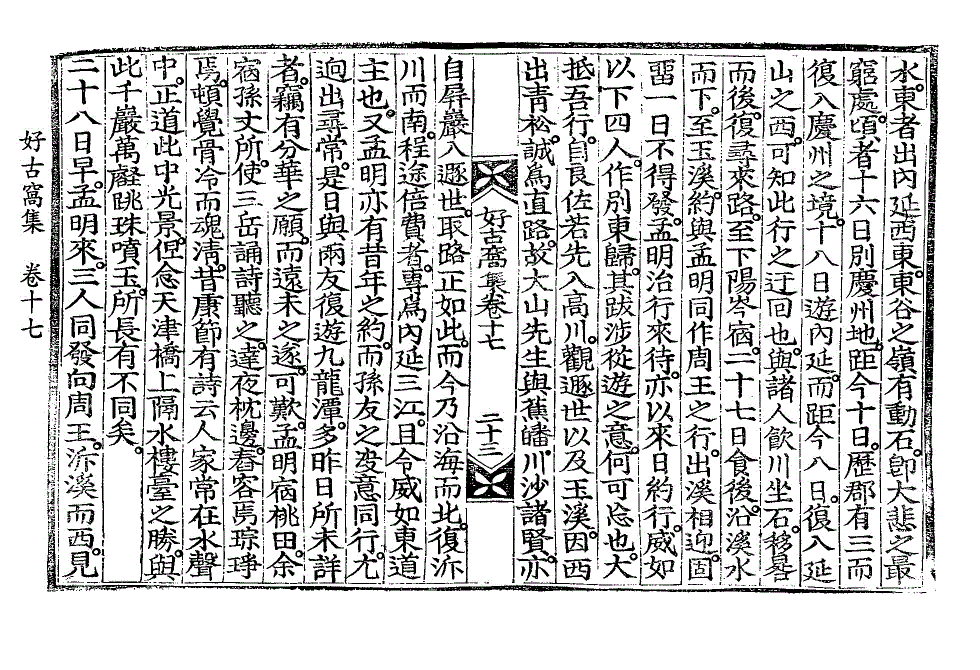 水。东者出内延西东。东谷之岭有动石。即大悲之最穷处。顷者十六日别庆州地。距今十日。历郡有三而复入庆州之境。十八日游内延。而距今八日。复入延山之西。可知此行之迂回也。与诸人饮川坐石。移晷而后。复寻来路。至下阳岑宿。二十七日食后。沿溪水而下。至玉溪。约与孟明同作周王之行。出溪相迎。固留一日不得发。孟明治行来待。亦以来日约行。威如以下四人。别作东归。其跋涉从游之意。何可忘也。大抵吾行。自良佐若先入高川。观遁世以及玉溪。因西出青松。诚为直路。故大山先生与蕉皤,川沙诸贤。亦自屏岩入遁世。取路正如此。而今乃沿海而北。复溯川而南。程途倍费者。专为内延三江。且令威如东道主也。又孟明亦有昔年之约。而孙友之决意同行。尤迥出寻常。是日与两友复游九龙潭。多昨日所未详者。窃有分华之愿。而远未之遂。可叹。孟明宿桃田。余宿孙丈所。使三岳诵诗听之。达夜枕边。舂容焉琮琤焉。顿觉骨冷而魂清。昔康节有诗云人家常在水声中。正道此中光景。但念天津桥上隔水楼台之胜。与此千岩万壑跳珠喷玉。所长有不同矣。
水。东者出内延西东。东谷之岭有动石。即大悲之最穷处。顷者十六日别庆州地。距今十日。历郡有三而复入庆州之境。十八日游内延。而距今八日。复入延山之西。可知此行之迂回也。与诸人饮川坐石。移晷而后。复寻来路。至下阳岑宿。二十七日食后。沿溪水而下。至玉溪。约与孟明同作周王之行。出溪相迎。固留一日不得发。孟明治行来待。亦以来日约行。威如以下四人。别作东归。其跋涉从游之意。何可忘也。大抵吾行。自良佐若先入高川。观遁世以及玉溪。因西出青松。诚为直路。故大山先生与蕉皤,川沙诸贤。亦自屏岩入遁世。取路正如此。而今乃沿海而北。复溯川而南。程途倍费者。专为内延三江。且令威如东道主也。又孟明亦有昔年之约。而孙友之决意同行。尤迥出寻常。是日与两友复游九龙潭。多昨日所未详者。窃有分华之愿。而远未之遂。可叹。孟明宿桃田。余宿孙丈所。使三岳诵诗听之。达夜枕边。舂容焉琮琤焉。顿觉骨冷而魂清。昔康节有诗云人家常在水声中。正道此中光景。但念天津桥上隔水楼台之胜。与此千岩万壑跳珠喷玉。所长有不同矣。二十八日早。孟明来。三人同发向周王。溯溪而西。见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4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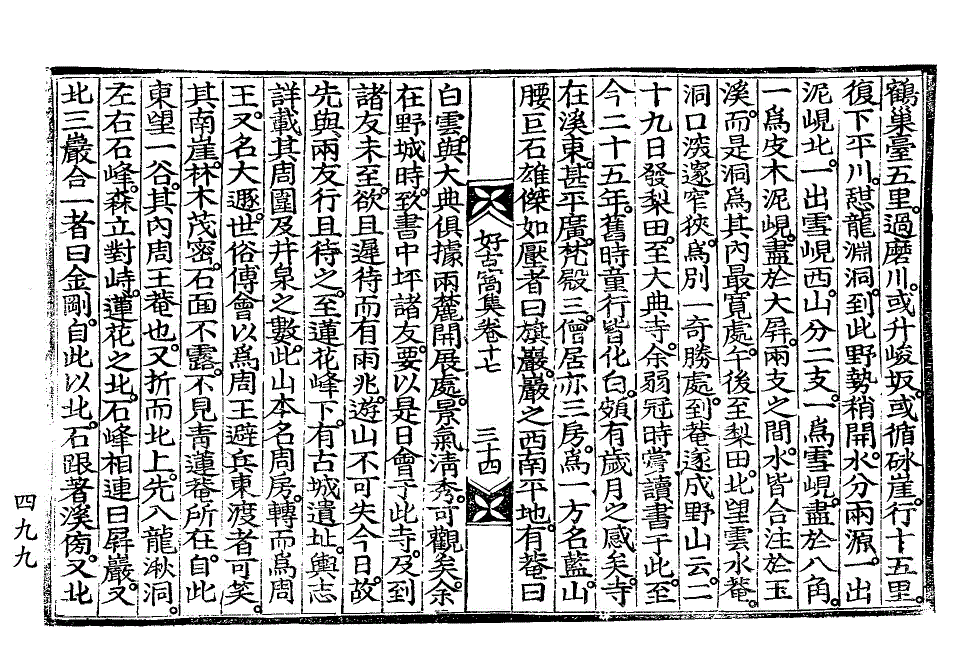 鹤巢台五里。过磨川。或升峻坂。或循砯崖。行十五里。复下平川。憩龙渊洞。到此野势稍开。水分两源。一出泥岘北。一出雪岘西。山分二支。一为雪岘。尽于八角。一为皮木泥岘。尽于大屏。两支之间。水皆合注于玉溪。而是洞为其内最宽处。午后至梨田。北望云水庵。洞口深邃窄狭。为别一奇胜处。到庵遂成野山云。二十九日发梨田。至大典寺。余弱冠时尝读书于此。至今二十五年。旧时童行皆化白。颇有岁月之感矣。寺在溪东。甚平广。梵殿三。僧居亦三房。为一方名蓝。山腰巨石雄杰如压者曰旗岩。岩之西南平地。有庵曰白云。与大典俱据两麓开展处。景气清秀。可观矣。余在野城时。致书中坪诸友。要以是日会于此寺。及到诸友未至。欲且迟待而有雨兆。游山不可失今日。故先与两友行且待之。至莲花峰下。有古城遗址。舆志详载其周围及井泉之数。此山本名周房。转而为周王。又名大遁。世俗傅会以为周王避兵东渡者可笑。其南崖。林木茂密。石面不露。不见青莲庵所在。自此东望一谷。其内周王庵也。又折而北上。先入龙湫洞。左右石峰。森立对峙。莲花之北。石峰相连曰屏岩。又北三岩合一者曰金刚。自此以北。石跟著溪傍。又北
鹤巢台五里。过磨川。或升峻坂。或循砯崖。行十五里。复下平川。憩龙渊洞。到此野势稍开。水分两源。一出泥岘北。一出雪岘西。山分二支。一为雪岘。尽于八角。一为皮木泥岘。尽于大屏。两支之间。水皆合注于玉溪。而是洞为其内最宽处。午后至梨田。北望云水庵。洞口深邃窄狭。为别一奇胜处。到庵遂成野山云。二十九日发梨田。至大典寺。余弱冠时尝读书于此。至今二十五年。旧时童行皆化白。颇有岁月之感矣。寺在溪东。甚平广。梵殿三。僧居亦三房。为一方名蓝。山腰巨石雄杰如压者曰旗岩。岩之西南平地。有庵曰白云。与大典俱据两麓开展处。景气清秀。可观矣。余在野城时。致书中坪诸友。要以是日会于此寺。及到诸友未至。欲且迟待而有雨兆。游山不可失今日。故先与两友行且待之。至莲花峰下。有古城遗址。舆志详载其周围及井泉之数。此山本名周房。转而为周王。又名大遁。世俗傅会以为周王避兵东渡者可笑。其南崖。林木茂密。石面不露。不见青莲庵所在。自此东望一谷。其内周王庵也。又折而北上。先入龙湫洞。左右石峰。森立对峙。莲花之北。石峰相连曰屏岩。又北三岩合一者曰金刚。自此以北。石跟著溪傍。又北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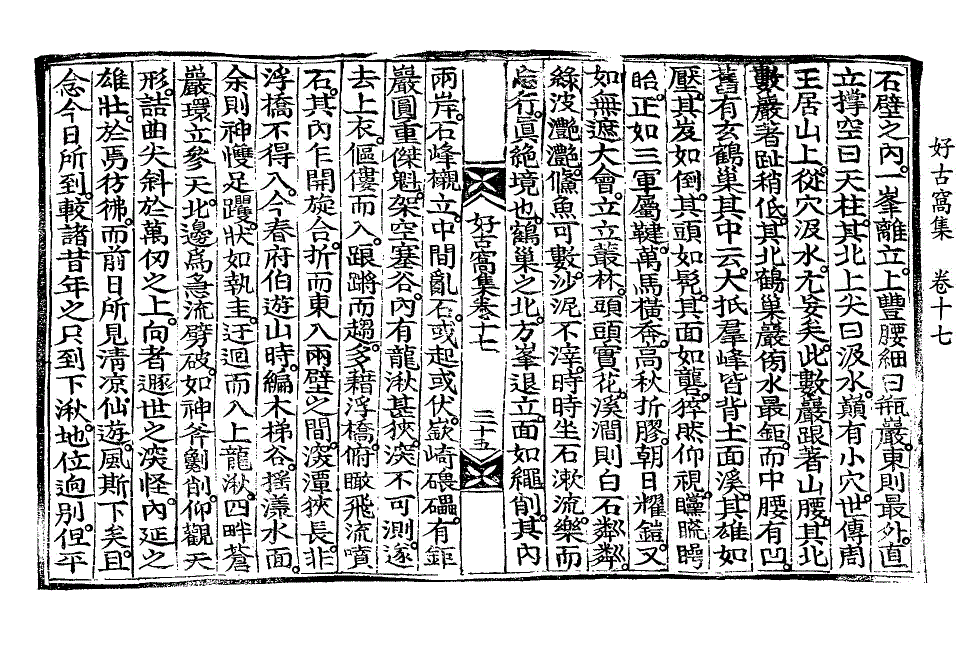 石壁之内。一峰离立。上丰腰细曰瓶岩。东则最外。直立撑空曰天柱。其北上尖曰汲水。巅有小穴。世传周王居山上。从穴汲水。尤妄矣。此数岩跟著山腰。其北数岩著趾稍低。其北鹤巢岩傍水最钜。而中腰有凹。旧有玄鹤巢其中云。大抵群峰皆背土面溪。其雄如压。其岌如倒。其头如髡。其面如砻。猝然仰视。矘𥉂𥈭眙。正如三军属鞬。万马横奔。高秋折胶。朝日耀铠。又如无遮大会。立立丛林。头头实花。溪涧则白石粼粼。绿波滟滟。鯈鱼可数。沙泥不滓。时时坐石漱流。乐而忘行。真绝境也。鹤巢之北。方峰退立。面如绳削。其内两岸。石峰衬立。中间乱石。或起或伏。嵚崎碨礧。有钜岩圆重杰魁。架空塞谷。内有龙湫甚狭。深不可测。遂去上衣。伛偻而入。踉蹡而趋。多藉浮桥。俯瞰飞流喷石。其内乍开旋合。折而东入两壁之间。深潭狭长。非浮桥不得入。今春府伯游山时。编木梯谷。摇漾水面。余则神𢥠足躩。状如执圭。迂回而入上龙湫。四畔苍岩环立参天。北边为急流劈破。如神斧劖削。仰观天形。诘曲尖斜于万仞之上。向者遁世之深怪。内延之雄壮。于焉彷佛。而前日所见清凉,仙游。风斯下矣。且念今日所到。较诸昔年之只到下湫。地位迥别。但平
石壁之内。一峰离立。上丰腰细曰瓶岩。东则最外。直立撑空曰天柱。其北上尖曰汲水。巅有小穴。世传周王居山上。从穴汲水。尤妄矣。此数岩跟著山腰。其北数岩著趾稍低。其北鹤巢岩傍水最钜。而中腰有凹。旧有玄鹤巢其中云。大抵群峰皆背土面溪。其雄如压。其岌如倒。其头如髡。其面如砻。猝然仰视。矘𥉂𥈭眙。正如三军属鞬。万马横奔。高秋折胶。朝日耀铠。又如无遮大会。立立丛林。头头实花。溪涧则白石粼粼。绿波滟滟。鯈鱼可数。沙泥不滓。时时坐石漱流。乐而忘行。真绝境也。鹤巢之北。方峰退立。面如绳削。其内两岸。石峰衬立。中间乱石。或起或伏。嵚崎碨礧。有钜岩圆重杰魁。架空塞谷。内有龙湫甚狭。深不可测。遂去上衣。伛偻而入。踉蹡而趋。多藉浮桥。俯瞰飞流喷石。其内乍开旋合。折而东入两壁之间。深潭狭长。非浮桥不得入。今春府伯游山时。编木梯谷。摇漾水面。余则神𢥠足躩。状如执圭。迂回而入上龙湫。四畔苍岩环立参天。北边为急流劈破。如神斧劖削。仰观天形。诘曲尖斜于万仞之上。向者遁世之深怪。内延之雄壮。于焉彷佛。而前日所见清凉,仙游。风斯下矣。且念今日所到。较诸昔年之只到下湫。地位迥别。但平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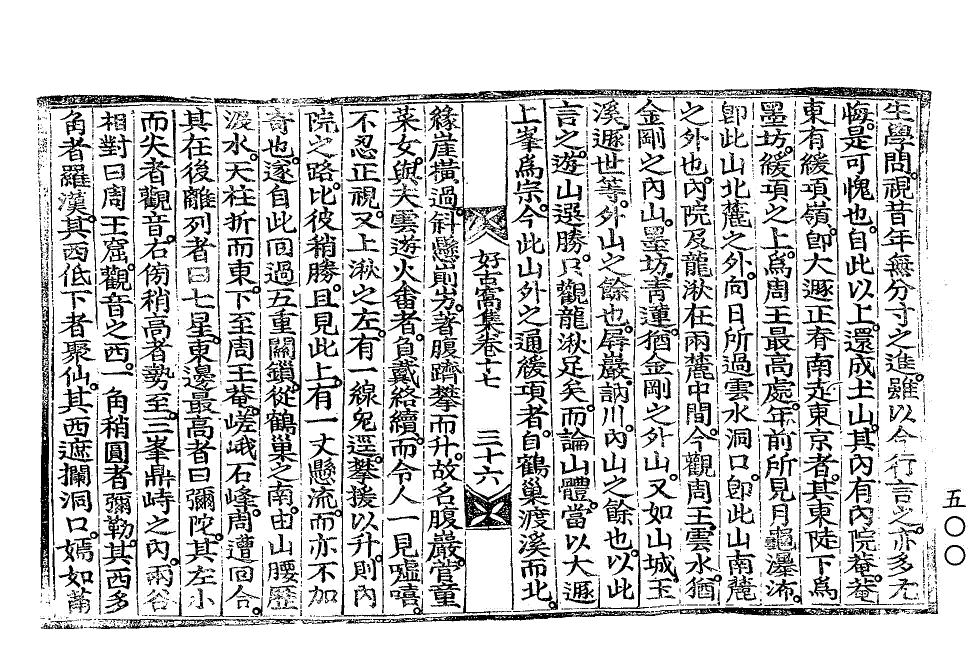 生学问。视昔年无分寸之进。虽以今行言之。亦多尤悔。是可愧也。自此以上。还成土山。其内有内院庵。庵东有缓项岭。即大遁正脊南走东京者。其东陡下为墨坊。缓项之上。为周王最高处。年前所见月龟瀑㳍。即此山北麓之外。向日所过云水洞口。即此山南麓之外也。内院及龙湫在两麓中间。今观周王,云水。犹金刚之内山。墨坊,青莲。犹金刚之外山。又如山城,玉溪,遁世等。外山之馀也。屏岩,讷川。内山之馀也。以此言之。游山选胜。只观龙湫足矣。而论山体。当以大遁上峰为宗。今此山外之通缓项者。自鹤巢渡溪而北。缘崖横过。斜悬崱屴。著腹跻攀而升。故名腹岩。菅童菜女。与夫云游火畬者。负戴络续。而令人一见嘘嘻。不忍正视。又上湫之左。有一线兔径。攀援以升。则内院之路。比彼稍胜。且见此上。有一丈悬流。而亦不加奇也。遂自此回过五重关锁。从鹤巢之南。由山腰历汲水。天柱折而东。下至周王庵。嵯峨石峰。周遭回合。其在后离列者曰七星。东边最高者曰弥陀。其左小而尖者观音。右傍稍高者势至。三峰鼎峙之内。两谷相对曰周王窟。观音之西。一角稍圆者弥勒。其西多角者罗汉。其西低下者聚仙。其西遮拦洞口。嫣如菡
生学问。视昔年无分寸之进。虽以今行言之。亦多尤悔。是可愧也。自此以上。还成土山。其内有内院庵。庵东有缓项岭。即大遁正脊南走东京者。其东陡下为墨坊。缓项之上。为周王最高处。年前所见月龟瀑㳍。即此山北麓之外。向日所过云水洞口。即此山南麓之外也。内院及龙湫在两麓中间。今观周王,云水。犹金刚之内山。墨坊,青莲。犹金刚之外山。又如山城,玉溪,遁世等。外山之馀也。屏岩,讷川。内山之馀也。以此言之。游山选胜。只观龙湫足矣。而论山体。当以大遁上峰为宗。今此山外之通缓项者。自鹤巢渡溪而北。缘崖横过。斜悬崱屴。著腹跻攀而升。故名腹岩。菅童菜女。与夫云游火畬者。负戴络续。而令人一见嘘嘻。不忍正视。又上湫之左。有一线兔径。攀援以升。则内院之路。比彼稍胜。且见此上。有一丈悬流。而亦不加奇也。遂自此回过五重关锁。从鹤巢之南。由山腰历汲水。天柱折而东。下至周王庵。嵯峨石峰。周遭回合。其在后离列者曰七星。东边最高者曰弥陀。其左小而尖者观音。右傍稍高者势至。三峰鼎峙之内。两谷相对曰周王窟。观音之西。一角稍圆者弥勒。其西多角者罗汉。其西低下者聚仙。其西遮拦洞口。嫣如菡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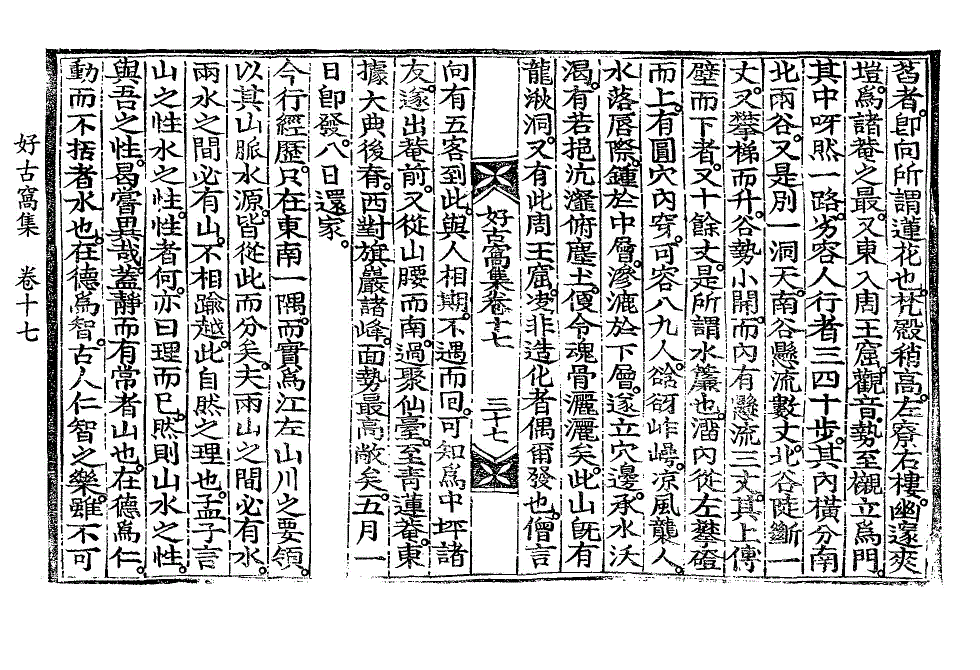 萏者。即向所谓莲花也。梵殿稍高。左寮右楼。幽邃爽垲。为诸庵之最。又东入周王窟。观音,势至衬立为门。其中呀然一路。劣容人行者三四十步。其内横分南北两谷。又是别一洞天。南谷悬流数丈。北谷陡断一丈。又攀梯而升。谷势小开。而内有悬流三丈。其上傅壁而下者。又十馀丈。是所谓水帘也。溜内从左攀磴而上。有圆穴内穿。可容八九人。谽谺岞崿。凉风袭人。水落唇际。钟于中层。渗漉于下层。遂立穴边。承水沃渴。有若挹沆瀣俯尘土。便令魂骨洒洒矣。此山既有龙湫洞。又有此周王窟。决非造化者偶尔发也。僧言向有五客到此。与人相期。不遇而回。可知为中坪诸友。遂出庵前。又从山腰而南。过聚仙台。至青莲庵。东据大典后脊。西对旗岩诸峰。面势最高敞矣。五月一日即发。八日还家。
萏者。即向所谓莲花也。梵殿稍高。左寮右楼。幽邃爽垲。为诸庵之最。又东入周王窟。观音,势至衬立为门。其中呀然一路。劣容人行者三四十步。其内横分南北两谷。又是别一洞天。南谷悬流数丈。北谷陡断一丈。又攀梯而升。谷势小开。而内有悬流三丈。其上傅壁而下者。又十馀丈。是所谓水帘也。溜内从左攀磴而上。有圆穴内穿。可容八九人。谽谺岞崿。凉风袭人。水落唇际。钟于中层。渗漉于下层。遂立穴边。承水沃渴。有若挹沆瀣俯尘土。便令魂骨洒洒矣。此山既有龙湫洞。又有此周王窟。决非造化者偶尔发也。僧言向有五客到此。与人相期。不遇而回。可知为中坪诸友。遂出庵前。又从山腰而南。过聚仙台。至青莲庵。东据大典后脊。西对旗岩诸峰。面势最高敞矣。五月一日即发。八日还家。今行经历。只在东南一隅。而实为江左山川之要领。以其山脉水源。皆从此而分矣。夫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不相踰越。此自然之理也。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性者何。亦曰理而已。然则山水之性。与吾之性。曷尝异哉。盖静而有常者山也。在德为仁。动而不括者水也。在德为智。古人仁智之乐。虽不可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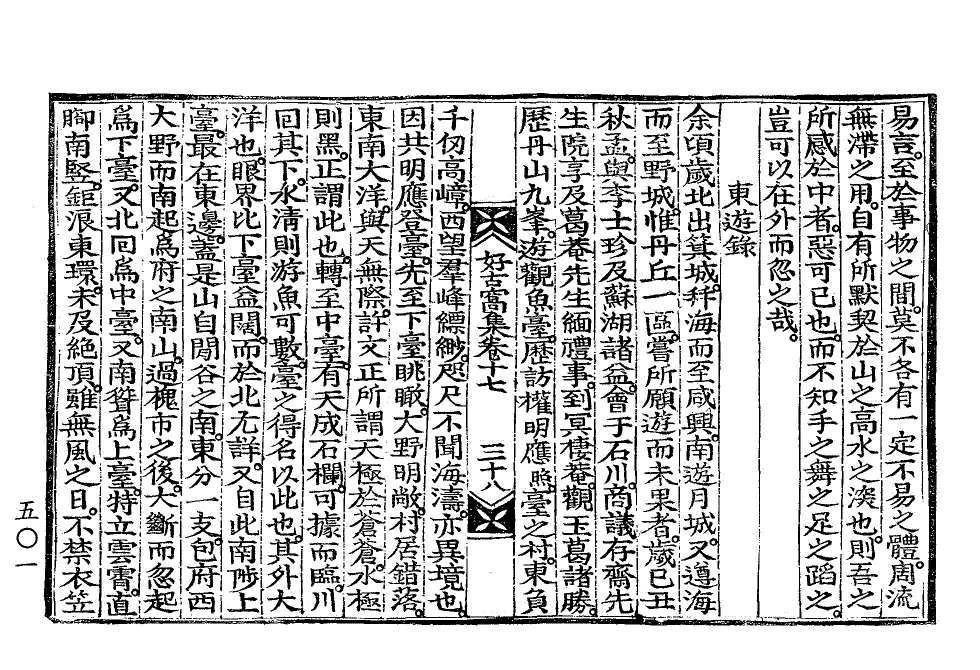 易言。至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一定不易之体。周流无滞之用。自有所默契于山之高水之深也。则吾之所感于中者。恶可已也。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岂可以在外而忽之哉。
易言。至于事物之间。莫不各有一定不易之体。周流无滞之用。自有所默契于山之高水之深也。则吾之所感于中者。恶可已也。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岂可以在外而忽之哉。东游录
余顷岁北出箕城。并海而至咸兴。南游月城。又遵海而至野城。惟丹丘一区。尝所愿游而未果者。岁己丑秋孟。与李士珍及苏湖诸益。会于石川。商议存斋先生院享及葛庵先生缅礼事。到冥栖庵。观玉葛诸胜。历丹山九峰。游观鱼台。历访权明应(照)。台之村。东负千仞高嶂。西望群峰缥缈。咫尺不闻海涛。亦异境也。因共明应登台。先至下台眺瞰。大野明敞。村居错落。东南大洋。与天无际。许文正所谓天极于苍苍。水极则黑。正谓此也。转至中台。有天成石栏。可据而临。川回其下。水清则游鱼可数。台之得名以此也。其外大洋也。眼界比下台益阔。而于北尤详。又自此南陟上台。最在东边。盖是山自閒谷之南。东分一支。包府西大野而南起为府之南山。过槐市之后。大断而忽起为下台。又北回为中台。又南耸为上台。特立云霄。直脚南竖。钜浪东环。未及绝顶。虽无风之日。不禁衣笠
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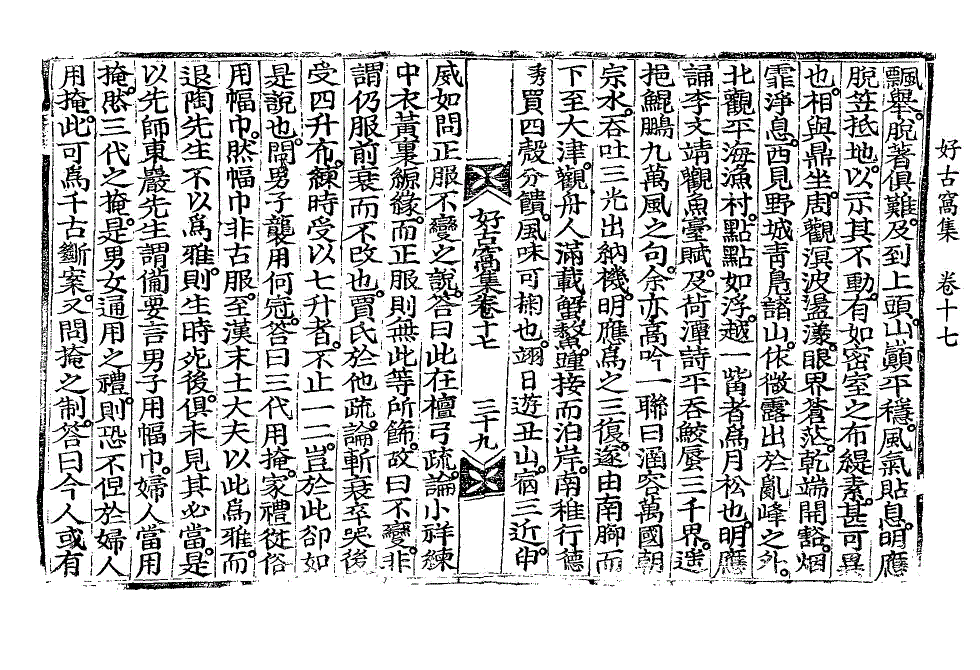 飘举。脱著俱难。及到上头。山巅平稳。风气贴息。明应脱笠抵地。以示其不动。有如密室之布缇素。甚可异也。相与鼎坐。周观溟波荡漾。眼界苍茫。乾端开豁。烟霏净息。西见野城青凫诸山。依微露出于乱峰之外。北观平海渔村。点点如浮。越一觜者为月松也。明应诵李文靖观鱼台赋。及荷潭诗平吞鲛蜃三千界。遥挹鲲鹏九万风之句。余亦高吟一联曰涵容万国朝宗水。吞吐三光出纳机。明应为之三复。遂由南脚而下至大津。观舟人满载蟹,鳌。踵接而泊岸。南稚行(德秀)买四壳分馈。风味可掬也。翊日游丑山。宿三近。申威如问正服不变之说。答曰此在檀弓疏。论小祥练中衣黄里縓缘。而正服则无此等所饰。故曰不变。非谓仍服前衰而不改也。贾氏于他疏。论斩衰卒哭后受四升布。练时受以七升者。不止一二。岂于此却如是说也。问男子袭用何冠。答曰三代用掩。家礼从俗用幅巾。然幅巾非古服。至汉末士大夫以此为雅。而退陶先生不以为雅。则生时死后。俱未见其必当。是以先师东岩先生谓备要言男子用幅巾。妇人当用掩。然三代之掩。是男女通用之礼。则恐不但于妇人用掩。此可为千古断案。又问掩之制。答曰今人或有
飘举。脱著俱难。及到上头。山巅平稳。风气贴息。明应脱笠抵地。以示其不动。有如密室之布缇素。甚可异也。相与鼎坐。周观溟波荡漾。眼界苍茫。乾端开豁。烟霏净息。西见野城青凫诸山。依微露出于乱峰之外。北观平海渔村。点点如浮。越一觜者为月松也。明应诵李文靖观鱼台赋。及荷潭诗平吞鲛蜃三千界。遥挹鲲鹏九万风之句。余亦高吟一联曰涵容万国朝宗水。吞吐三光出纳机。明应为之三复。遂由南脚而下至大津。观舟人满载蟹,鳌。踵接而泊岸。南稚行(德秀)买四壳分馈。风味可掬也。翊日游丑山。宿三近。申威如问正服不变之说。答曰此在檀弓疏。论小祥练中衣黄里縓缘。而正服则无此等所饰。故曰不变。非谓仍服前衰而不改也。贾氏于他疏。论斩衰卒哭后受四升布。练时受以七升者。不止一二。岂于此却如是说也。问男子袭用何冠。答曰三代用掩。家礼从俗用幅巾。然幅巾非古服。至汉末士大夫以此为雅。而退陶先生不以为雅。则生时死后。俱未见其必当。是以先师东岩先生谓备要言男子用幅巾。妇人当用掩。然三代之掩。是男女通用之礼。则恐不但于妇人用掩。此可为千古断案。又问掩之制。答曰今人或有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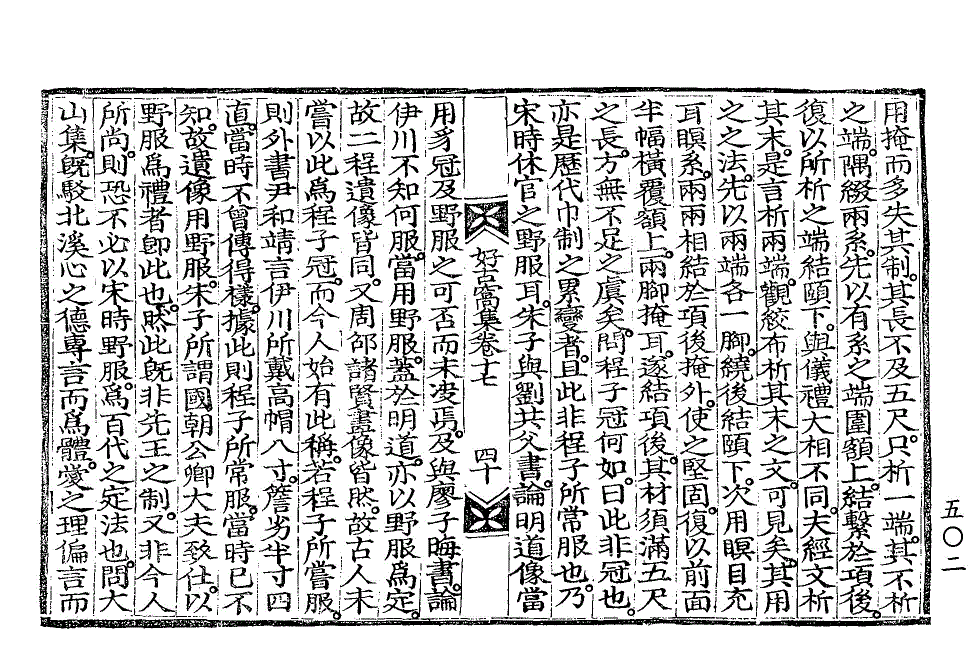 用掩而多失其制。其长不及五尺。只析一端。其不析之端。隅缀两系。先以有系之端围额上。结系于项后。复以所析之端结颐下。与仪礼大相不同。夫经文析其末。是言析两端。观绞布析其末之文。可见矣。其用之之法。先以两端各一脚。绕后结颐下。次用瞑目充耳瞑系。两两相结于项后掩外。使之坚固。复以前面半幅横覆额上。两脚掩耳。遂结项后。其材须满五尺之长。方无不足之虞矣。问程子冠何如。曰此非冠也。亦是历代巾制之累变者。且此非程子所常服也。乃宋时休官之野服耳。朱子与刘共父书。论明道像当用豸冠及野服之可否而未决焉。及与廖子晦书。论伊川不知何服。当用野服。盖于明道。亦以野服为定。故二程遗像皆同。又周邵诸贤画像皆然。故古人未尝以此为程子冠。而今人始有此称。若程子所尝服。则外书尹和靖言伊川所戴高帽八寸。檐劣半寸四直。当时不曾传得样。据此则程子所常服。当时已不知。故遗像用野服。朱子所谓国朝公卿大夫致仕。以野服为礼者即此也。然此既非先王之制。又非今人所尚。则恐不必以宋时野服。为百代之定法也。问大山集。既驳北溪心之德专言而为体。爱之理偏言而
用掩而多失其制。其长不及五尺。只析一端。其不析之端。隅缀两系。先以有系之端围额上。结系于项后。复以所析之端结颐下。与仪礼大相不同。夫经文析其末。是言析两端。观绞布析其末之文。可见矣。其用之之法。先以两端各一脚。绕后结颐下。次用瞑目充耳瞑系。两两相结于项后掩外。使之坚固。复以前面半幅横覆额上。两脚掩耳。遂结项后。其材须满五尺之长。方无不足之虞矣。问程子冠何如。曰此非冠也。亦是历代巾制之累变者。且此非程子所常服也。乃宋时休官之野服耳。朱子与刘共父书。论明道像当用豸冠及野服之可否而未决焉。及与廖子晦书。论伊川不知何服。当用野服。盖于明道。亦以野服为定。故二程遗像皆同。又周邵诸贤画像皆然。故古人未尝以此为程子冠。而今人始有此称。若程子所尝服。则外书尹和靖言伊川所戴高帽八寸。檐劣半寸四直。当时不曾传得样。据此则程子所常服。当时已不知。故遗像用野服。朱子所谓国朝公卿大夫致仕。以野服为礼者即此也。然此既非先王之制。又非今人所尚。则恐不必以宋时野服。为百代之定法也。问大山集。既驳北溪心之德专言而为体。爱之理偏言而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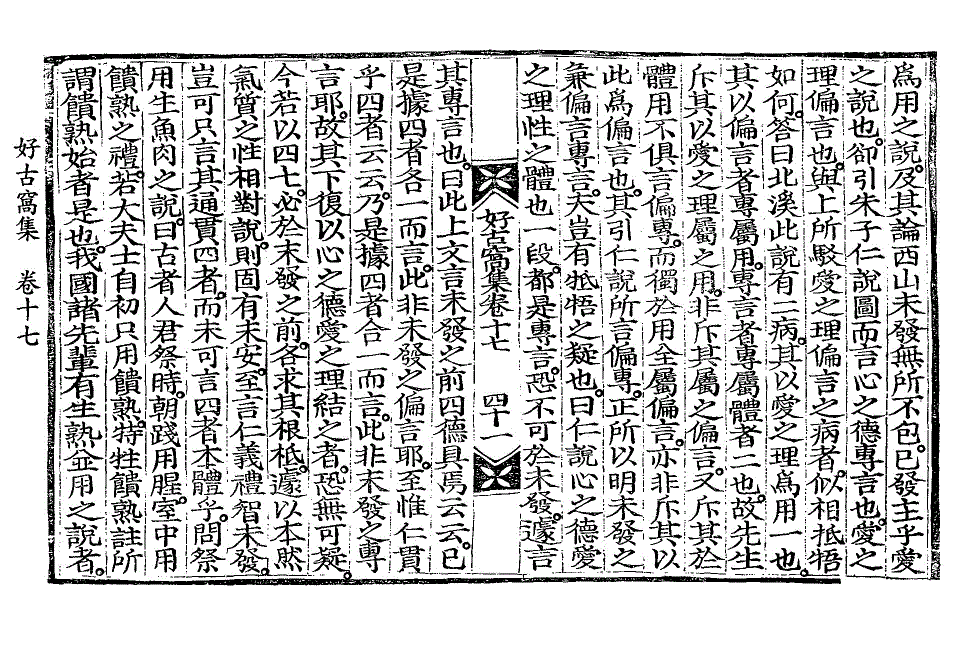 为用之说。及其论西山未发无所不包。已发主乎爱之说也。却引朱子仁说图而言心之德专言也。爱之理偏言也。与上所驳爱之理偏言之病者。似相抵牾如何。答曰北溪此说有二病。其以爱之理为用一也。其以偏言者专属用。专言者专属体者二也。故先生斥其以爱之理属之用。非斥其属之偏言。又斥其于体用不俱言偏专。而独于用全属偏言。亦非斥其以此为偏言也。其引仁说所言偏专。正所以明未发之兼偏言专言。夫岂有牴牾之疑也。曰仁说心之德爱之理性之体也一段。都是专言。恐不可于未发。遽言其专言也。曰此上文言未发之前四德具焉云云。已是据四者各一而言。此非未发之偏言耶。至惟仁贯乎四者云云。乃是据四者合一而言。此非未发之专言耶。故其下复以心之德爱之理结之者。恐无可疑。今若以四七。必于未发之前。各求其根柢。遽以本然气质之性相对说。则固有未安。至言仁义礼智未发。岂可只言其通贯四者。而未可言四者本体乎。问祭用生鱼肉之说。曰古者人君祭时。朝践用腥。室中用馈熟之礼。若大夫士自初只用馈熟。特牲馈熟注所谓馈熟始者是也。我国诸先辈有生熟并用之说者。
为用之说。及其论西山未发无所不包。已发主乎爱之说也。却引朱子仁说图而言心之德专言也。爱之理偏言也。与上所驳爱之理偏言之病者。似相抵牾如何。答曰北溪此说有二病。其以爱之理为用一也。其以偏言者专属用。专言者专属体者二也。故先生斥其以爱之理属之用。非斥其属之偏言。又斥其于体用不俱言偏专。而独于用全属偏言。亦非斥其以此为偏言也。其引仁说所言偏专。正所以明未发之兼偏言专言。夫岂有牴牾之疑也。曰仁说心之德爱之理性之体也一段。都是专言。恐不可于未发。遽言其专言也。曰此上文言未发之前四德具焉云云。已是据四者各一而言。此非未发之偏言耶。至惟仁贯乎四者云云。乃是据四者合一而言。此非未发之专言耶。故其下复以心之德爱之理结之者。恐无可疑。今若以四七。必于未发之前。各求其根柢。遽以本然气质之性相对说。则固有未安。至言仁义礼智未发。岂可只言其通贯四者。而未可言四者本体乎。问祭用生鱼肉之说。曰古者人君祭时。朝践用腥。室中用馈熟之礼。若大夫士自初只用馈熟。特牲馈熟注所谓馈熟始者是也。我国诸先辈有生熟并用之说者。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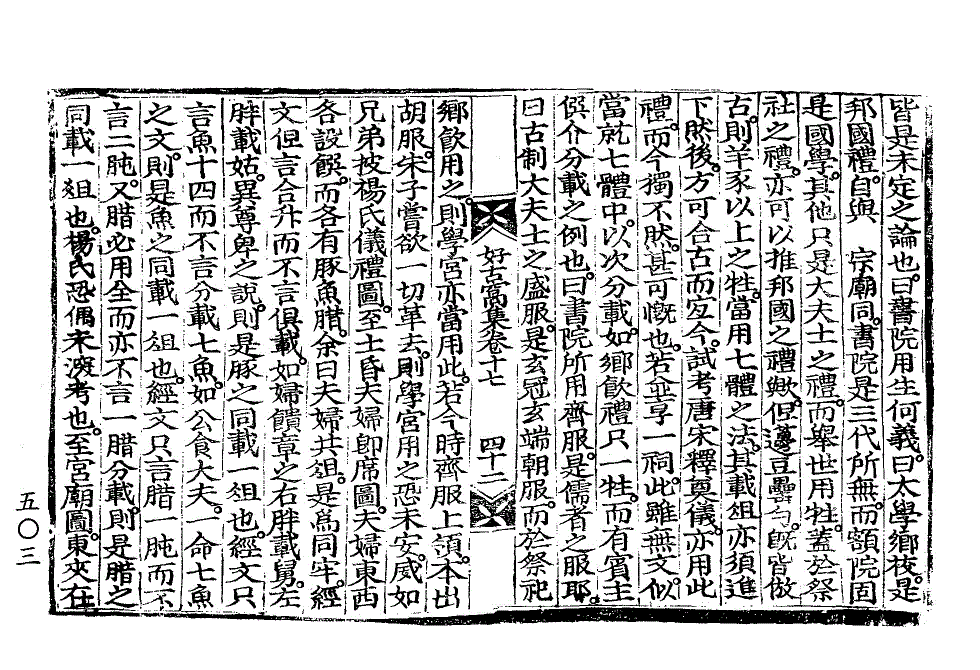 皆是未定之论也。曰书院用生何义。曰太学乡校。是邦国礼。自与 宗庙同。书院是三代所无。而额院固是国学。其他只是大夫士之礼。而举世用牲。盖于祭社之礼。亦可以推邦国之礼欤。但笾豆罍勺。既皆仿古。则羊豕以上之牲。当用七体之法。其载俎亦须进下然后。方可合古而宜今。试考唐宋释奠仪。亦用此礼。而今独不然。甚可慨也。若并享一祠。此虽无文。似当就七体中。以次分载。如乡饮礼只一牲。而有宾主僎介分载之例也。曰书院所用齐服。是儒者之服耶。曰古制大夫士之盛服。是玄冠玄端朝服。而于祭祀乡饮用之。则学宫亦当用此。若今时齐服上领。本出胡服。朱子尝欲一切革去。则学宫用之恐未安。威如兄弟披杨氏仪礼图。至士昏夫妇即席图。夫妇东西各设馔。而各有豚鱼腊。余曰夫妇共俎。是为同牢。经文但言合升而不言俱载。如妇馈章之右胖载舅。左胖载姑。异尊卑之说。则是豚之同载一俎也。经文只言鱼十四而不言分载七鱼。如公食大夫。一命七鱼之文。则是鱼之同载一俎也。经文只言腊一肫而不言二肫。又腊必用全而亦不言一腊分载。则是腊之同载一俎也。杨氏恐偶未深考也。至宫庙图。东夹在
皆是未定之论也。曰书院用生何义。曰太学乡校。是邦国礼。自与 宗庙同。书院是三代所无。而额院固是国学。其他只是大夫士之礼。而举世用牲。盖于祭社之礼。亦可以推邦国之礼欤。但笾豆罍勺。既皆仿古。则羊豕以上之牲。当用七体之法。其载俎亦须进下然后。方可合古而宜今。试考唐宋释奠仪。亦用此礼。而今独不然。甚可慨也。若并享一祠。此虽无文。似当就七体中。以次分载。如乡饮礼只一牲。而有宾主僎介分载之例也。曰书院所用齐服。是儒者之服耶。曰古制大夫士之盛服。是玄冠玄端朝服。而于祭祀乡饮用之。则学宫亦当用此。若今时齐服上领。本出胡服。朱子尝欲一切革去。则学宫用之恐未安。威如兄弟披杨氏仪礼图。至士昏夫妇即席图。夫妇东西各设馔。而各有豚鱼腊。余曰夫妇共俎。是为同牢。经文但言合升而不言俱载。如妇馈章之右胖载舅。左胖载姑。异尊卑之说。则是豚之同载一俎也。经文只言鱼十四而不言分载七鱼。如公食大夫。一命七鱼之文。则是鱼之同载一俎也。经文只言腊一肫而不言二肫。又腊必用全而亦不言一腊分载。则是腊之同载一俎也。杨氏恐偶未深考也。至宫庙图。东夹在好古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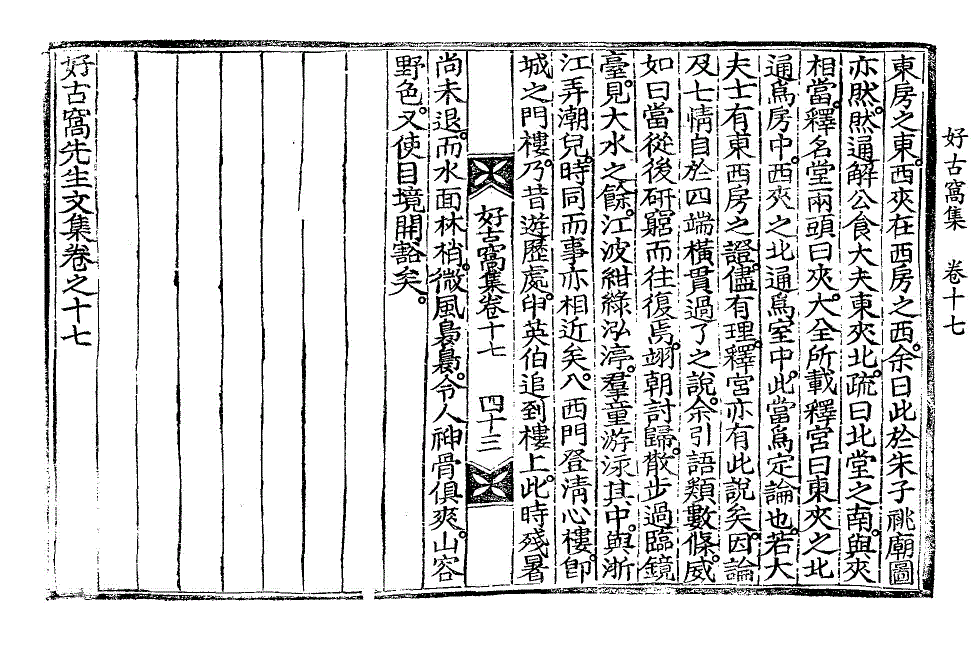 东房之东。西夹在西房之西。余曰此于朱子祧庙图亦然。然通解公食大夫东夹北。疏曰北堂之南。与夹相当。释名堂两头曰夹。大全所载释宫曰东夹之北通为房中。西夹之北通为室中。此当为定论也。若大夫士有东西房之證。尽有理。释宫亦有此说矣。因论及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之说。余引语类数条。威如曰当从后研穷而往复焉。翊朝讨归。散步过临镜台。见大水之馀。江波绀绿泓渟。群童游泳其中。与浙江弄潮儿。时同而事亦相近矣。入西门登清心楼。即城之门楼。乃昔游历处。申英伯追到楼上。此时残暑尚未退。而水面林梢。微风袅袅。令人神骨俱爽。山容野色。又使目境开豁矣。
东房之东。西夹在西房之西。余曰此于朱子祧庙图亦然。然通解公食大夫东夹北。疏曰北堂之南。与夹相当。释名堂两头曰夹。大全所载释宫曰东夹之北通为房中。西夹之北通为室中。此当为定论也。若大夫士有东西房之證。尽有理。释宫亦有此说矣。因论及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之说。余引语类数条。威如曰当从后研穷而往复焉。翊朝讨归。散步过临镜台。见大水之馀。江波绀绿泓渟。群童游泳其中。与浙江弄潮儿。时同而事亦相近矣。入西门登清心楼。即城之门楼。乃昔游历处。申英伯追到楼上。此时残暑尚未退。而水面林梢。微风袅袅。令人神骨俱爽。山容野色。又使目境开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