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中庸讲义条对[二](抄 启应制○丁巳)
中庸讲义条对[二](抄 启应制○丁巳)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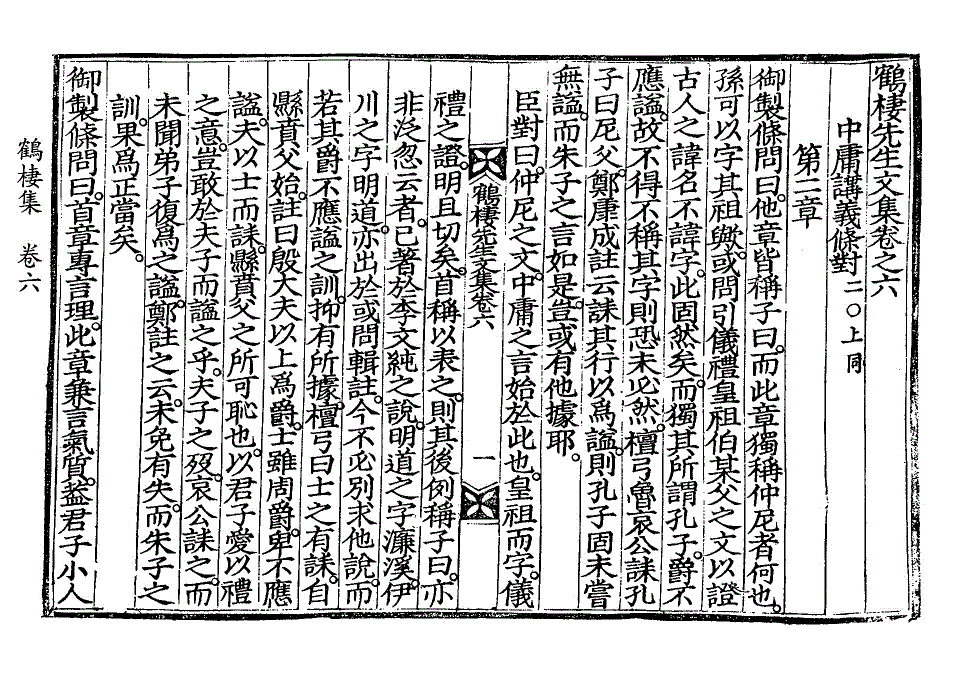 第二章
第二章御制条问曰。他章皆称子曰。而此章独称仲尼者何也。孙可以字其祖欤。或问引仪礼皇祖伯某父之文以證古人之讳名不讳字。此固然矣。而独其所谓孔子。爵不应谥。故不得不称其字则恐未必然。檀弓鲁哀公诔孔子曰尼父。郑康成注云诔其行以为谥。则孔子固未尝无谥。而朱子之言如是。岂或有他据耶。
臣对曰。仲尼之文。中庸之言始于此也。皇祖而字。仪礼之證。明且切矣。首称以表之。则其后例称子曰。亦非泛忽云者。已著于李文纯之说。明道之字濂溪。伊川之字明道。亦出于或问辑注。今不必别求他说。而若其爵不应谥之训。抑有所据。檀弓曰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注曰殷大夫以上为爵。士虽周爵。卑不应谥。夫以士而诔。县贲父之所可耻也。以君子爱以礼之意。岂敢于夫子而谥之乎。夫子之殁。哀公诔之。而未闻弟子复为之谥。郑注之云。未免有失。而朱子之训。果为正当矣。
御制条问曰。首章专言理。此章兼言气质。盖君子小人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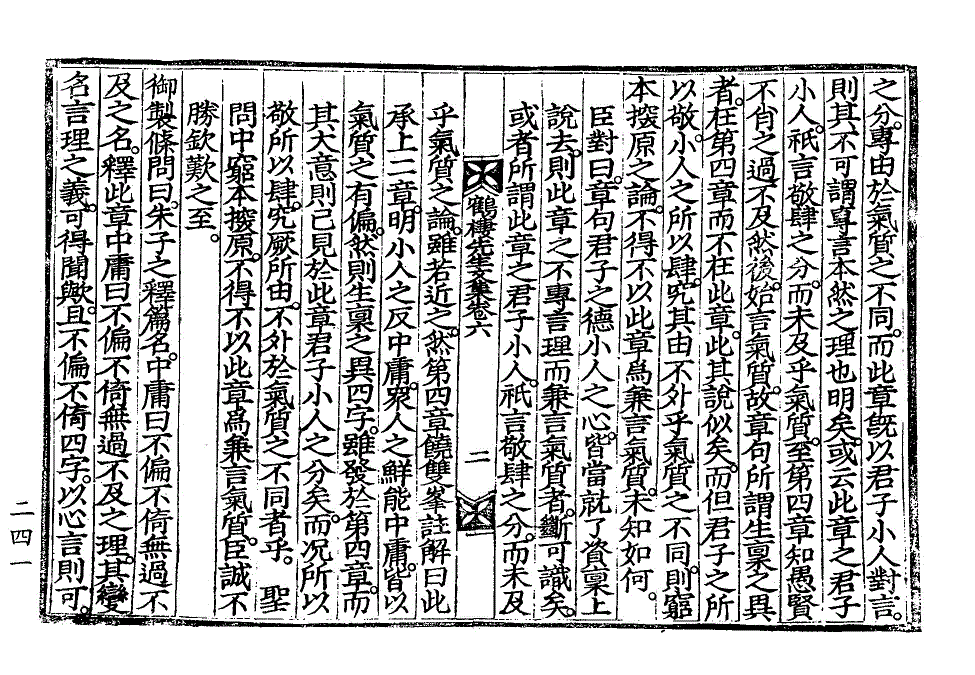 之分。专由于气质之不同。而此章既以君子小人对言。则其不可谓专言本然之理也明矣。或云此章之君子小人。祇言敬肆之分。而未及乎气质。至第四章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然后。始言气质。故章句所谓生禀之异者。在第四章而不在此章。此其说似矣。而但君子之所以敬。小人之所以肆。究其由不外乎气质之不同。则穷本探原之论。不得不以此章为兼言气质。未知如何。
之分。专由于气质之不同。而此章既以君子小人对言。则其不可谓专言本然之理也明矣。或云此章之君子小人。祇言敬肆之分。而未及乎气质。至第四章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然后。始言气质。故章句所谓生禀之异者。在第四章而不在此章。此其说似矣。而但君子之所以敬。小人之所以肆。究其由不外乎气质之不同。则穷本探原之论。不得不以此章为兼言气质。未知如何。臣对曰。章句君子之德小人之心。皆当就了资禀上说去。则此章之不专言理而兼言气质者。断可识矣。或者所谓此章之君子小人。祇言敬肆之分。而未及乎气质之论。虽若近之。然第四章饶双峰注解曰此承上二章。明小人之反中庸。众人之鲜能中庸。皆以气质之有偏。然则生禀之异四字。虽发于第四章。而其大意则已见于此章君子小人之分矣。而况所以敬所以肆。究厥所由。不外于气质之不同者乎。 圣问中穷本探原。不得不以此章为兼言气质。臣诚不胜钦叹之至。
御制条问曰。朱子之释篇名。中庸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释此章中庸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理。其变名言理之义。可得闻欤。且不偏不倚四字。以心言则可。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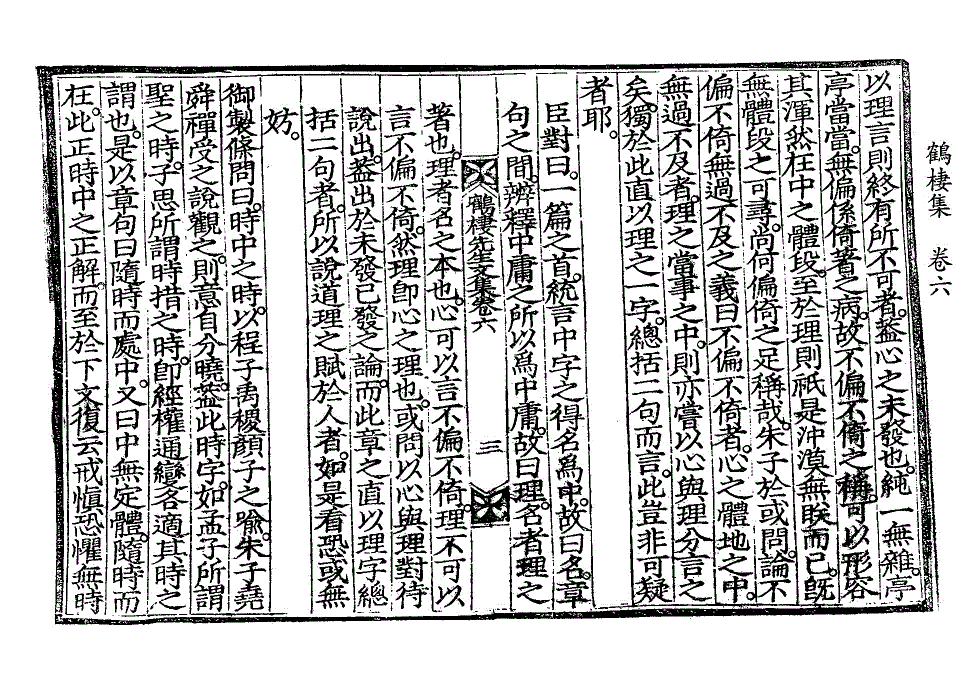 以理言则终有所不可者。盖心之未发也。纯一无杂。亭亭当当。无偏系倚著之病。故不偏不倚之称。可以形容其浑然在中之体段。至于理则祇是冲漠无眹而已。既无体段之可寻。尚何偏倚之足称哉。朱子于或问。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曰不偏不倚者。心之体地之中。无过不及者。理之当事之中。则亦尝以心与理分言之矣。独于此直以理之一字。总括二句而言。此岂非可疑者耶。
以理言则终有所不可者。盖心之未发也。纯一无杂。亭亭当当。无偏系倚著之病。故不偏不倚之称。可以形容其浑然在中之体段。至于理则祇是冲漠无眹而已。既无体段之可寻。尚何偏倚之足称哉。朱子于或问。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曰不偏不倚者。心之体地之中。无过不及者。理之当事之中。则亦尝以心与理分言之矣。独于此直以理之一字。总括二句而言。此岂非可疑者耶。臣对曰。一篇之首。统言中字之得名为中。故曰名。章句之间。辨释中庸之所以为中庸。故曰理。名者理之著也。理者名之本也。心可以言不偏不倚。理不可以言不偏不倚。然理即心之理也。或问以心与理对待说出。盖出于未发已发之论。而此章之直以理字总括二句者。所以说道理之赋于人者。如是看恐或无妨。
御制条问曰。时中之时。以程子禹稷颜子之喻。朱子尧舜禅受之说观之。则意自分晓。盖此时字。如孟子所谓圣之时。子思所谓时措之时。即经权通变各适其时之谓也。是以章句曰随时而处中。又曰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此正时中之正解。而至于下文复云戒慎恐惧无时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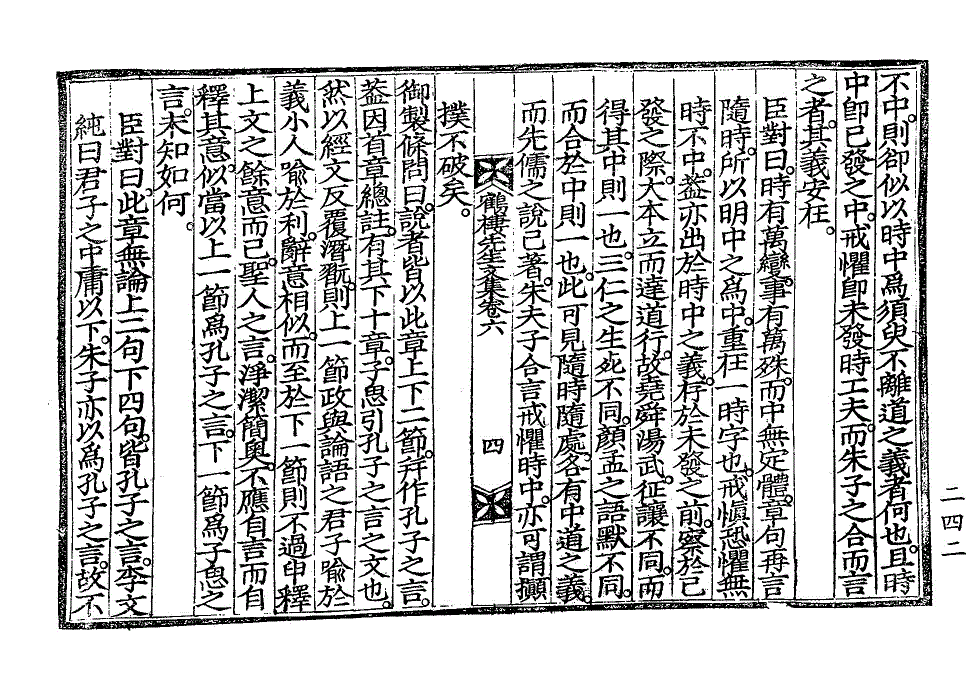 不中。则却似以时中为须臾不离道之义者何也。且时中即已发之中。戒惧即未发时工夫。而朱子之合而言之者。其义安在。
不中。则却似以时中为须臾不离道之义者何也。且时中即已发之中。戒惧即未发时工夫。而朱子之合而言之者。其义安在。臣对曰。时有万变。事有万殊。而中无定体。章句再言随时。所以明中之为中。重在一时字也。戒慎恐惧无时不中。盖亦出于时中之义。存于未发之前。察于已发之际。大本立而达道行。故尧舜汤武。征让不同。而得其中则一也。三仁之生死不同。颜孟之语默不同。而合于中则一也。此可见随时随处。各有中道之义。而先儒之说已著。朱夫子合言戒惧时中。亦可谓攧扑不破矣。
御制条问曰。说者皆以此章上下二节。并作孔子之言。盖因首章总注。有其下十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之文也。然以经文反覆潜玩。则上一节政与论语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辞意相似。而至于下一节则不过申释上文之馀意而已。圣人之言。净洁简奥。不应自言而自释其意。似当以上一节为孔子之言。下一节为子思之言。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章无论上二句下四句。皆孔子之言。李文纯曰君子之中庸以下。朱子亦以为孔子之言。故不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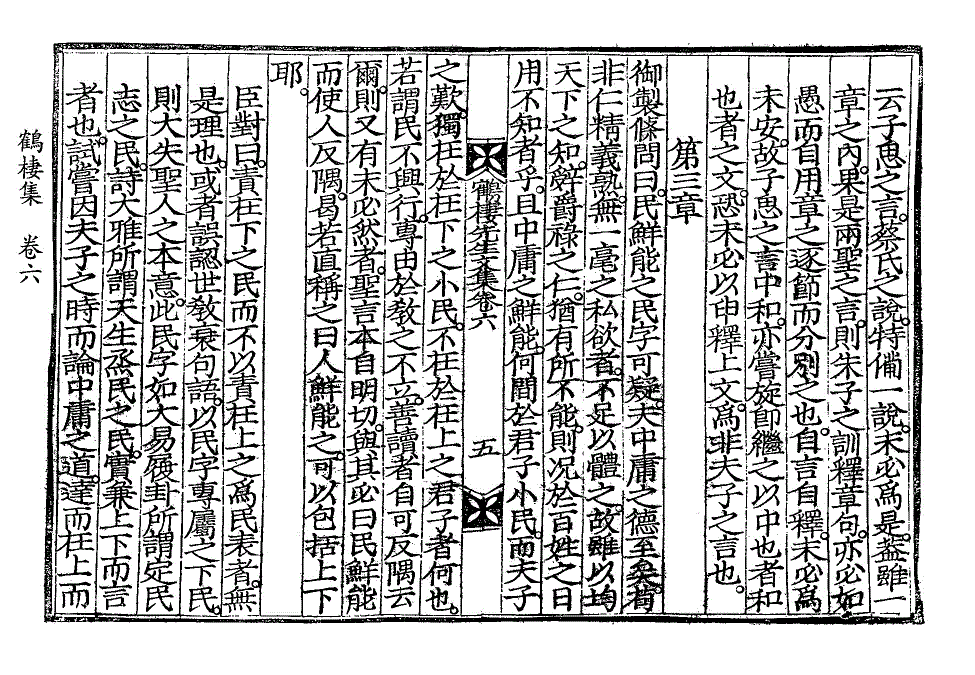 云子思之言。蔡氏之说。特备一说。未必为是。盖虽一章之内。果是两圣之言。则朱子之训释章句。亦必如愚而自用章之逐节而分别之也。自言自释。未必为未安。故子思之言中和。亦尝旋即继之以中也者和也者之文。恐未必以申释上文。为非夫子之言也。
云子思之言。蔡氏之说。特备一说。未必为是。盖虽一章之内。果是两圣之言。则朱子之训释章句。亦必如愚而自用章之逐节而分别之也。自言自释。未必为未安。故子思之言中和。亦尝旋即继之以中也者和也者之文。恐未必以申释上文。为非夫子之言也。第三章
御制条问曰。民鲜能之民字可疑。夫中庸之德至矣。苟非仁精义熟。无一毫之私欲者。不足以体之。故虽以均天下之知。辞爵禄之仁。犹有所不能。则况于百姓之日用不知者乎。且中庸之鲜能。何间于君子小民。而夫子之叹。独在于在下之小民。不在于在上之君子者何也。若谓民不兴行。专由于教之不立。善读者自可反隅云尔。则又有未必然者。圣言本自明切。与其必曰民鲜能而使人反隅。曷若直称之曰人鲜能之。可以包括上下耶。
臣对曰。责在下之民而不以责在上之为民表者。无是理也。或者误认世教衰句语。以民字专属之下民。则大失圣人之本意。此民字如大易履卦所谓定民志之民。诗大雅所谓天生烝民之民。实兼上下而言者也。试尝因夫子之时而论中庸之道。达而在上而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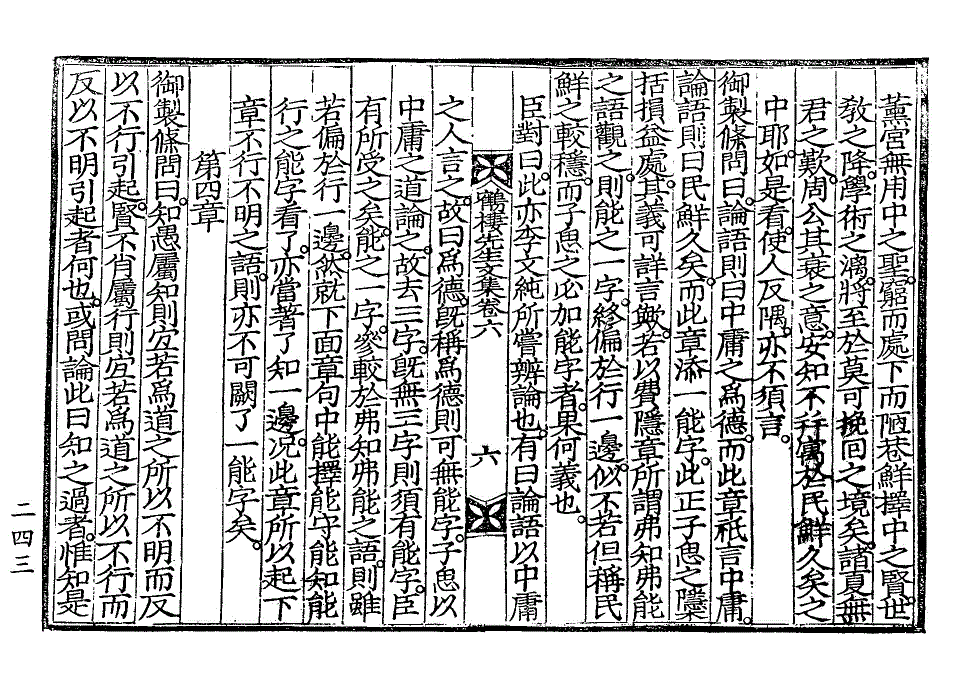 薰宫无用中之圣。穷而处下而陋巷鲜择中之贤。世教之降。学术之漓。将至于莫可挽回之境矣。诸夏无君之叹。周公其衰之意。安知不并寓于民鲜久矣之中耶。如是看。使人反隅。亦不须言。
薰宫无用中之圣。穷而处下而陋巷鲜择中之贤。世教之降。学术之漓。将至于莫可挽回之境矣。诸夏无君之叹。周公其衰之意。安知不并寓于民鲜久矣之中耶。如是看。使人反隅。亦不须言。御制条问曰。论语则曰中庸之为德。而此章祇言中庸。论语则曰民鲜久矣。而此章添一能字。此正子思之檃括损益处。其义可详言欤。若以费隐章所谓弗知弗能之语观之。则能之一字。终偏于行一边。似不若但称民鲜之较稳。而子思之必加能字者。果何义也。
臣对曰。此亦李文纯所尝辨论也。有曰论语以中庸之人言之。故曰为德。既称为德则可无能字。子思以中庸之道论之。故去三字。既无三字则须有能字。臣有所受之矣。能之一字。参较于弗知弗能之语。则虽若偏于行一边。然就下面章句中能择能守能知能行之能字看了。亦当著了知一边。况此章所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语。则亦不可阙了一能字矣。
第四章
御制条问曰。知愚属知则宜若为道之所以不明而反以不行引起。贤不肖属行则宜若为道之所以不行而反以不明引起者何也。或问论此曰知之过者。惟知是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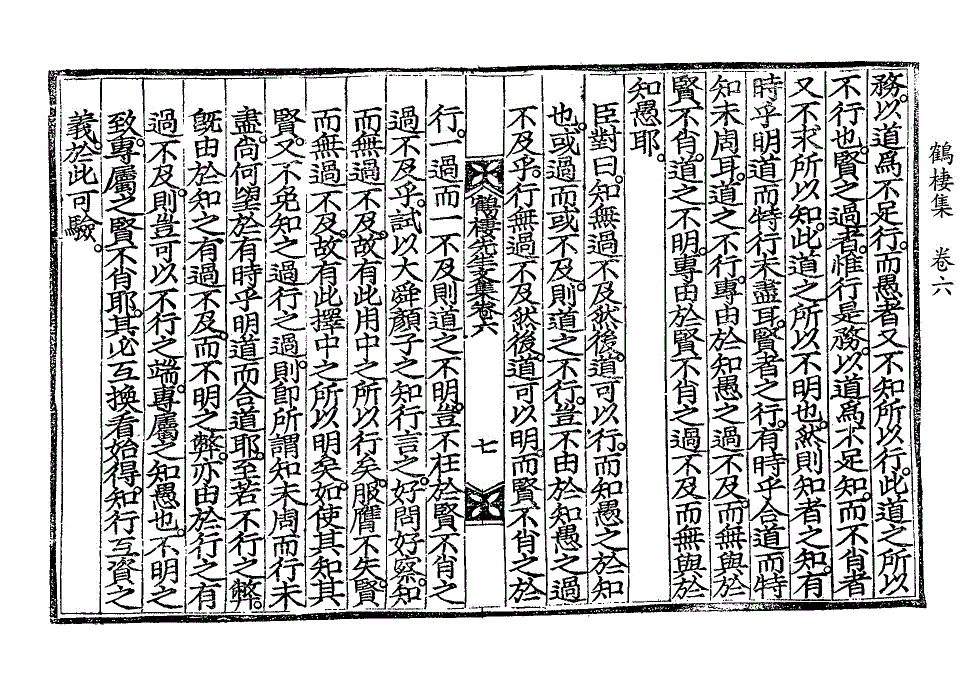 务。以道为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贤之过者。惟行是务。以道为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则知者之知。有时乎明道而特行未尽耳。贤者之行。有时乎合道而特知未周耳。道之不行。专由于知愚之过不及。而无与于贤不肖。道之不明。专由于贤不肖之过不及而无与于知愚耶。
务。以道为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贤之过者。惟行是务。以道为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则知者之知。有时乎明道而特行未尽耳。贤者之行。有时乎合道而特知未周耳。道之不行。专由于知愚之过不及。而无与于贤不肖。道之不明。专由于贤不肖之过不及而无与于知愚耶。臣对曰。知无过不及然后。道可以行。而知愚之于知也。或过而或不及。则道之不行。岂不由于知愚之过不及乎。行无过不及然后。道可以明。而贤不肖之于行。一过而一不及则道之不明。岂不在于贤不肖之过不及乎。试以大舜颜子之知行言之。好问好察。知而无过不及。故有此用中之所以行矣。服膺不失。贤而无过不及。故有此择中之所以明矣。如使其知其贤。又不免知之过行之过。则即所谓知未周而行未尽。尚何望于有时乎明道而合道耶。至若不行之弊。既由于知之有过不及。而不明之弊。亦由于行之有过不及。则岂可以不行之端。专属之知愚也。不明之致。专属之贤不肖耶。其必互换看始得。知行互资之义。于此可验。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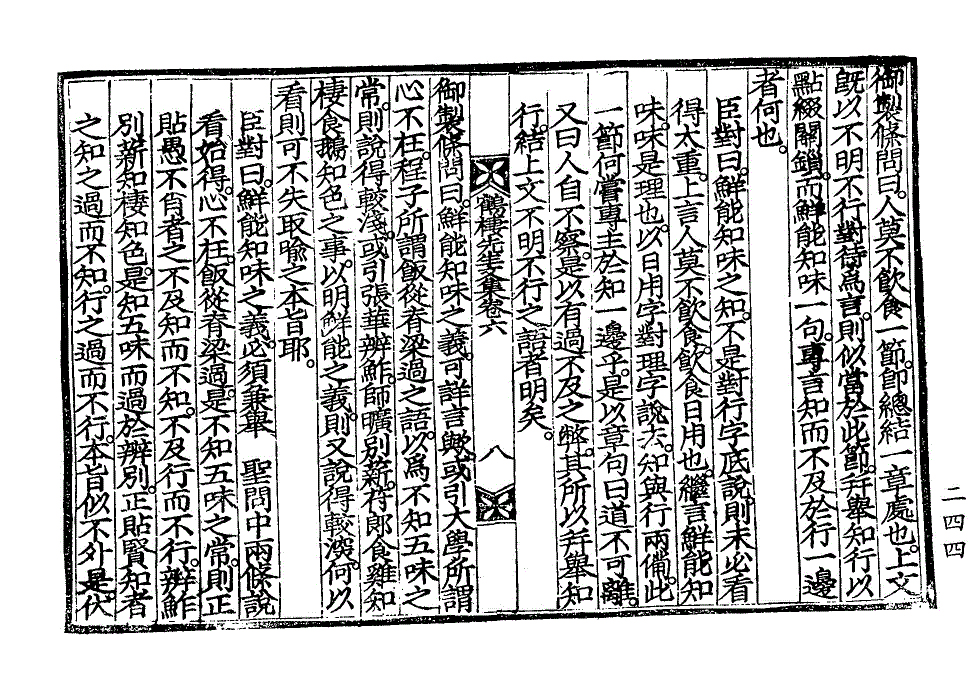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人莫不饮食一节。即总结一章处也。上文既以不明不行对待为言。则似当于此节。并举知行以点缀关锁。而鲜能知味一句。专言知而不及于行一边者何也。
御制条问曰。人莫不饮食一节。即总结一章处也。上文既以不明不行对待为言。则似当于此节。并举知行以点缀关锁。而鲜能知味一句。专言知而不及于行一边者何也。臣对曰。鲜能知味之知。不是对行字底说。则未必看得太重。上言人莫不饮食。饮食日用也。继言鲜能知味。味是理也。以日用字对理字说去。知与行两备。此一节何尝专主于知一边乎。是以章句曰道不可离。又曰人自不察。是以有过不及之弊。其所以并举知行。结上文不明不行之语者明矣。
御制条问曰。鲜能知味之义。可详言欤。或引大学所谓心不在。程子所谓饭从脊梁过之语。以为不知五味之常。则说得较浅。或引张华辨鲊。师旷别薪。苻郎食鸡知栖食鹅知色之事。以明鲜能之义。则又说得较深。何以看则可不失取喻之本旨耶。
臣对曰。鲜能知味之义。必须兼举 圣问中两条说看始得。心不在。饭从脊梁过。是不知五味之常。则正贴愚不肖者之不及知而不知。不及行而不行。辨鲊别薪知栖知色。是知五味而过于辨别。正贴贤知者之知之过而不知。行之过而不行。本旨似不外是。伏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5H 页
 未知如何。
未知如何。第五章
御制条问曰。上章并举不明不行。而此章则独言不行者何也。盖上章之鲜能知味。专言知。此章之道其不行。专言行。两节合为一章则知行备矣。而上节则必属之上章。此节则必别为一章。是果有分属之不得不然者欤。试详言之。
臣对曰。以不明不行两句语。分排引起大舜颜子之事。故此章独言不行。而至第七章。又言不明也。且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过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苟能有如大舜之无过不及。则非知之过者。而道之所以行也。此其承上起下处。不得不别为一章。而不可混合于上节明矣。
第六章
御制条问曰。此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谓两端。指何处而言。所谓中者。举何地而言。说者或以两端为善恶之分。以中为两端之中。苟如是则舜之用中。乃是半善半恶。和是和非之论。其于经旨。不亦远哉。故章句曰于善之中。执其两端。又于语类力斥中折两端之说。此正朱子盛水不漏处。而大有功于圣学者也。然试以经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5L 页
 文临文顺解。则执其两端之其字。既承上文善恶而来。则所谓两端。似指善恶之两端。用其中之其字。既承上文两端二字而来。则所谓中者。似指两端之中。此诚可疑。何以则可以善观而无碍耶。
文临文顺解。则执其两端之其字。既承上文善恶而来。则所谓两端。似指善恶之两端。用其中之其字。既承上文两端二字而来。则所谓中者。似指两端之中。此诚可疑。何以则可以善观而无碍耶。臣对曰。执其两端。犹言把其两头。两头皆善处。而中者又其善之至也。以两端为善恶之分。以中为两端之中之说。叶氏辑注之辨。晦翁语类之證。极其分晓。执其两端之其字。既承上文隐恶扬善之语。用其中之其字。又承这个两端之语。则其必曰执其善之两端。而用其善之至。然后方可为善观而无碍矣。
御制条问曰。两端之不可分善恶。观于上文所谓隐恶扬善一句则意自分晓。盖以恶者既隐则两端之皆善可知也。然既谓之善则宜无得失之可分。而善之中又有两端之异者何也。朱子语类云若以厚薄论之。有极厚之说。有极薄之说。极厚者说是则用极厚之说。极薄者说是则用极薄之说。夫极厚极薄。若是相反。则一是一非。亦宜悬殊。而槩归之善一边。圣人所谓道一而已者。岂如是耶。
臣对曰。善之有两端。以彼此言则可。以得失言则不可。如天下事。甲者说东。乙者说西。甲乙东西。虽各不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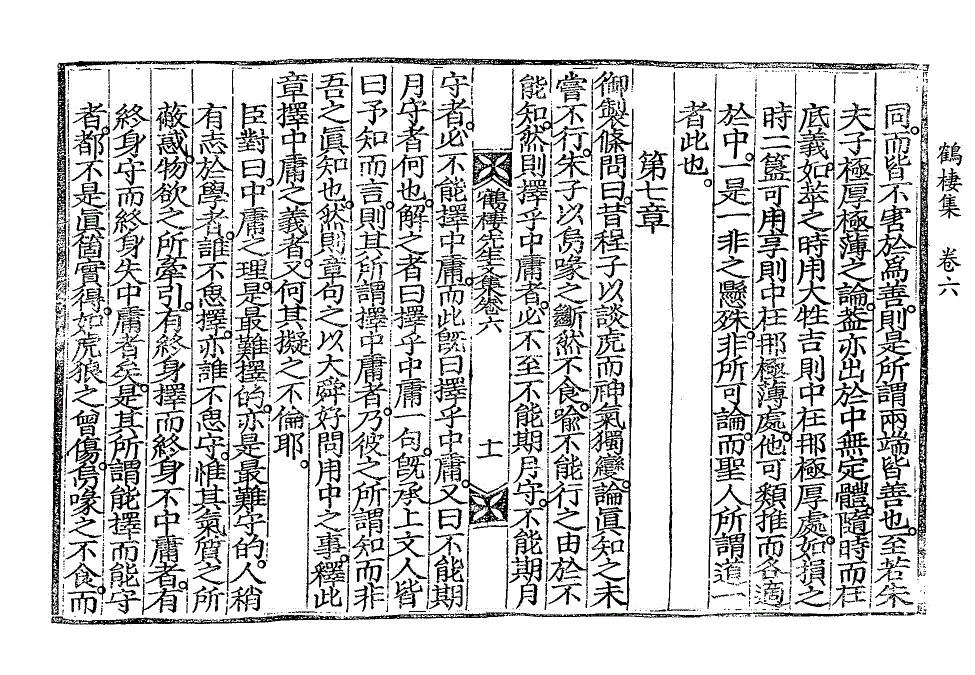 同。而皆不害于为善。则是所谓两端皆善也。至若朱夫子极厚极薄之论。盖亦出于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底义。如萃之时用大牲吉则中在那极厚处。如损之时二簋可用享则中在那极薄处。他可类推而各适于中。一是一非之悬殊。非所可论。而圣人所谓道一者此也。
同。而皆不害于为善。则是所谓两端皆善也。至若朱夫子极厚极薄之论。盖亦出于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底义。如萃之时用大牲吉则中在那极厚处。如损之时二簋可用享则中在那极薄处。他可类推而各适于中。一是一非之悬殊。非所可论。而圣人所谓道一者此也。第七章
御制条问曰。昔程子以谈虎而神气独变。论真知之未尝不行。朱子以乌喙之断然不食。喻不能行之由于不能知。然则择乎中庸者。必不至不能期月守。不能期月守者。必不能择中庸。而此既曰择乎中庸。又曰不能期月守者何也。解之者曰择乎中庸一句。既承上文人皆曰予知而言。则其所谓择中庸者。乃彼之所谓知而非吾之真知也。然则章句之以大舜好问用中之事。释此章择中庸之义者。又何其拟之不伦耶。
臣对曰。中庸之理。是最难择的。亦是最难守的。人稍有志于学者。谁不思择。亦谁不思守。惟其气质之所蔽惑。物欲之所牵引。有终身择而终身不中庸者。有终身守而终身失中庸者矣。是其所谓能择而能守者。都不是真个实得。如虎狼之曾伤。乌喙之不食。而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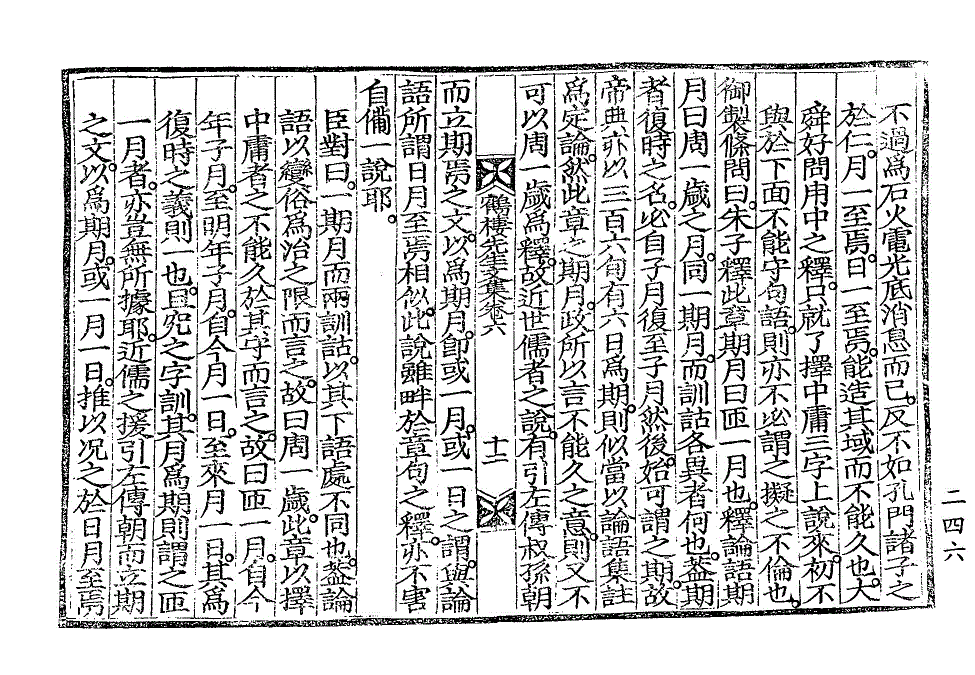 不过为石火电光底消息而已。反不如孔门诸子之于仁。月一至焉。日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大舜好问用中之释。只就了择中庸三字上说来。初不与于下面不能守句语。则亦不必谓之拟之不伦也。
不过为石火电光底消息而已。反不如孔门诸子之于仁。月一至焉。日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大舜好问用中之释。只就了择中庸三字上说来。初不与于下面不能守句语。则亦不必谓之拟之不伦也。御制条问曰。朱子释此章期月曰匝一月也。释论语期月曰周一岁之月。同一期月。而训诂各异者何也。盖期者复时之名。必自子月复至子月然后。始可谓之期。故帝典亦以三百六旬有六日为期。则似当以论语集注为定论。然此章之期月。政所以言不能久之意。则又不可以周一岁为释。故近世儒者之说。有引左传叔孙朝而立期焉之文。以为期月。即或一月。或一日之谓。与论语所谓日月至焉相似。此说虽畔于章句之释。亦不害自备一说耶。
臣对曰。一期月而两训诂。以其下语处不同也。盖论语以变俗为治之限而言之。故曰周一岁。此章以择中庸者之不能久于其守而言之。故曰匝一月。自今年子月。至明年子月。自今月一日。至来月一日。其为复时之义则一也。且究之字训。其月为期则谓之匝一月者。亦岂无所据耶。近儒之援引左传朝而立期之文。以为期月。或一月一日。推以况之于日月至焉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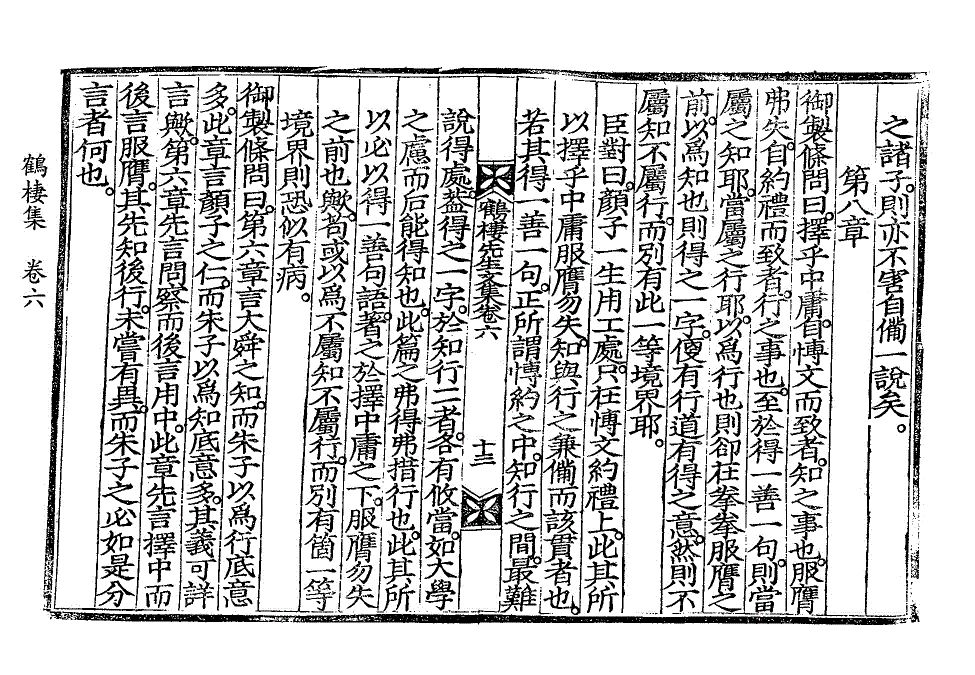 之诸子。则亦不害自备一说矣。
之诸子。则亦不害自备一说矣。第八章
御制条问曰。择乎中庸。自博文而致者。知之事也。服膺弗失。自约礼而致者。行之事也。至于得一善一句。则当属之知耶。当属之行耶。以为行也则却在拳拳服膺之前。以为知也则得之一字。便有行道有得之意。然则不属知不属行。而别有此一等境界耶。
臣对曰。颜子一生用工处。只在博文约礼上。此其所以择乎中庸服膺勿失。知与行之兼备而该贯者也。若其得一善一句。正所谓博约之中。知行之间。最难说得处。盖得之一字。于知行二者。各有攸当。如大学之虑而后能得知也。此篇之弗得弗措行也。此其所以必以得一善句语。著之于择中庸之下。服膺勿失之前也欤。苟或以为不属知不属行。而别有个一等境界则恐似有病。
御制条问曰。第六章言大舜之知。而朱子以为行底意多。此章言颜子之仁。而朱子以为知底意多。其义可详言欤。第六章先言问察而后言用中。此章先言择中而后言服膺。其先知后行。未尝有异。而朱子之必如是分言者何也。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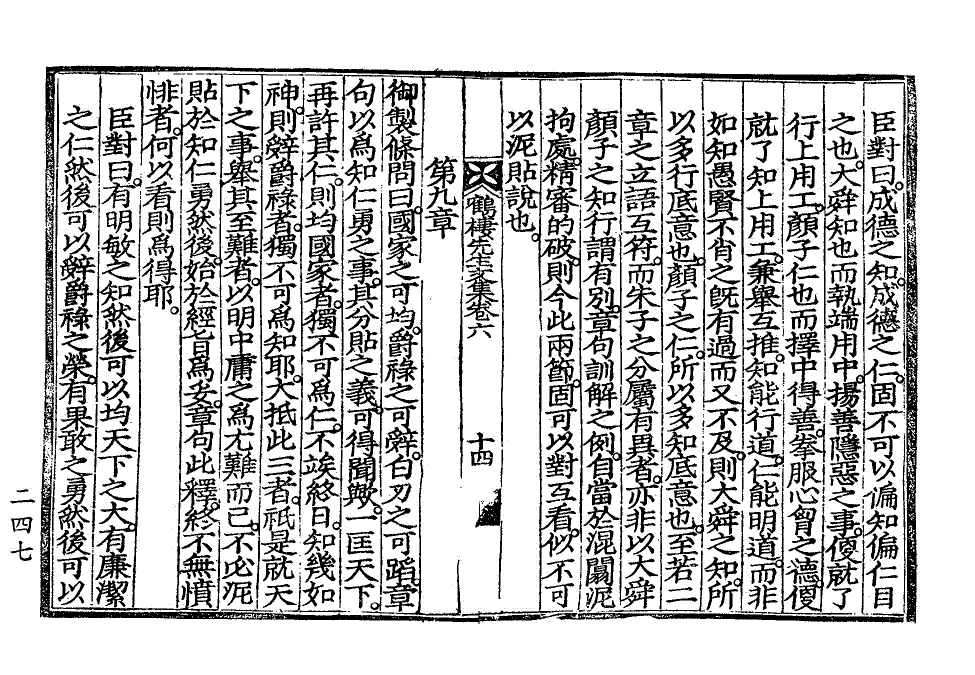 臣对曰。成德之知。成德之仁。固不可以偏知偏仁目之也。大舜知也而执端用中。扬善隐恶之事。便就了行上用工。颜子仁也而择中得善。拳服心胸之德。便就了知上用工。兼举互推。知能行道。仁能明道。而非如知愚贤不肖之既有过而又不及。则大舜之知。所以多行底意也。颜子之仁。所以多知底意也。至若二章之立语互符。而朱子之分属有异者。亦非以大舜颜子之知行谓有别。章句训解之例。自当于混阘泥拘处。精审的破。则今此两节。固可以对互看。似不可以泥贴说也。
臣对曰。成德之知。成德之仁。固不可以偏知偏仁目之也。大舜知也而执端用中。扬善隐恶之事。便就了行上用工。颜子仁也而择中得善。拳服心胸之德。便就了知上用工。兼举互推。知能行道。仁能明道。而非如知愚贤不肖之既有过而又不及。则大舜之知。所以多行底意也。颜子之仁。所以多知底意也。至若二章之立语互符。而朱子之分属有异者。亦非以大舜颜子之知行谓有别。章句训解之例。自当于混阘泥拘处。精审的破。则今此两节。固可以对互看。似不可以泥贴说也。第九章
御制条问曰。国家之可均。爵禄之可辞。白刃之可蹈。章句以为知仁勇之事。其分贴之义。可得闻欤。一匡天下。再许其仁。则均国家者。独不可为仁。不俟终日。知几如神。则辞爵禄者。独不可为知耶。大抵此三者。祇是就天下之事。举其至难者。以明中庸之为尤难而已。不必泥贴于知仁勇然后。始于经旨为妥。章句此释。终不无愤悱者。何以看则为得耶。
臣对曰。有明敏之知然后可以均天下之大。有廉洁之仁然后可以辞爵禄之荣。有果敢之勇然后可以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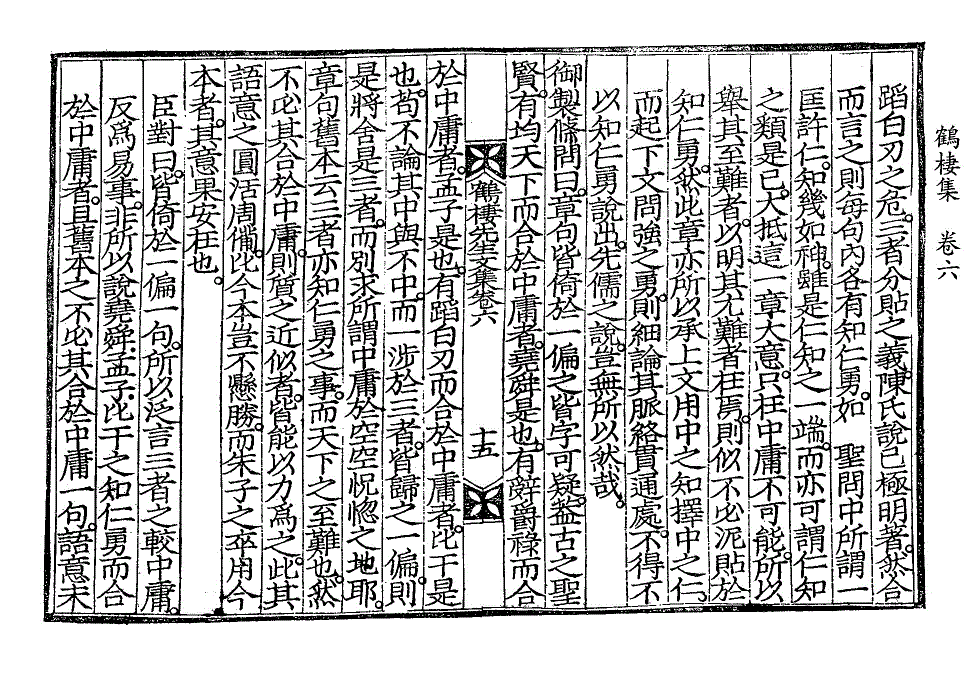 蹈白刃之危。三者分贴之义。陈氏说已极明著。然合而言之则每句内各有知仁勇。如 圣问中所谓一匡许仁。知几如神。虽是仁知之一端。而亦可谓仁知之类是已。大抵这一章大意。只在中庸不可能。所以举其至难者。以明其尤难者在焉。则似不必泥贴于知仁勇。然此章亦所以承上文用中之知择中之仁。而起下文问强之勇。则细论其脉络贯通处。不得不以知仁勇说出。先儒之说。岂无所以然哉。
蹈白刃之危。三者分贴之义。陈氏说已极明著。然合而言之则每句内各有知仁勇。如 圣问中所谓一匡许仁。知几如神。虽是仁知之一端。而亦可谓仁知之类是已。大抵这一章大意。只在中庸不可能。所以举其至难者。以明其尤难者在焉。则似不必泥贴于知仁勇。然此章亦所以承上文用中之知择中之仁。而起下文问强之勇。则细论其脉络贯通处。不得不以知仁勇说出。先儒之说。岂无所以然哉。御制条问曰。章句皆倚于一偏之皆字可疑。盖古之圣贤。有均天下而合于中庸者。尧舜是也。有辞爵禄而合于中庸者。孟子是也。有蹈白刃而合于中庸者。比干是也。苟不论其中与不中。而一涉于三者。皆归之一偏。则是将舍是三者。而别求所谓中庸于空空恍惚之地耶。章句旧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而天下之至难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此其语意之圆活周备。比今本岂不悬胜。而朱子之卒用今本者。其意果安在也。
臣对曰。皆倚于一偏一句。所以泛言三者之较中庸。反为易事。非所以说尧舜,孟子,比干之知仁勇而合于中庸者。且旧本之不必其合于中庸一句。语意未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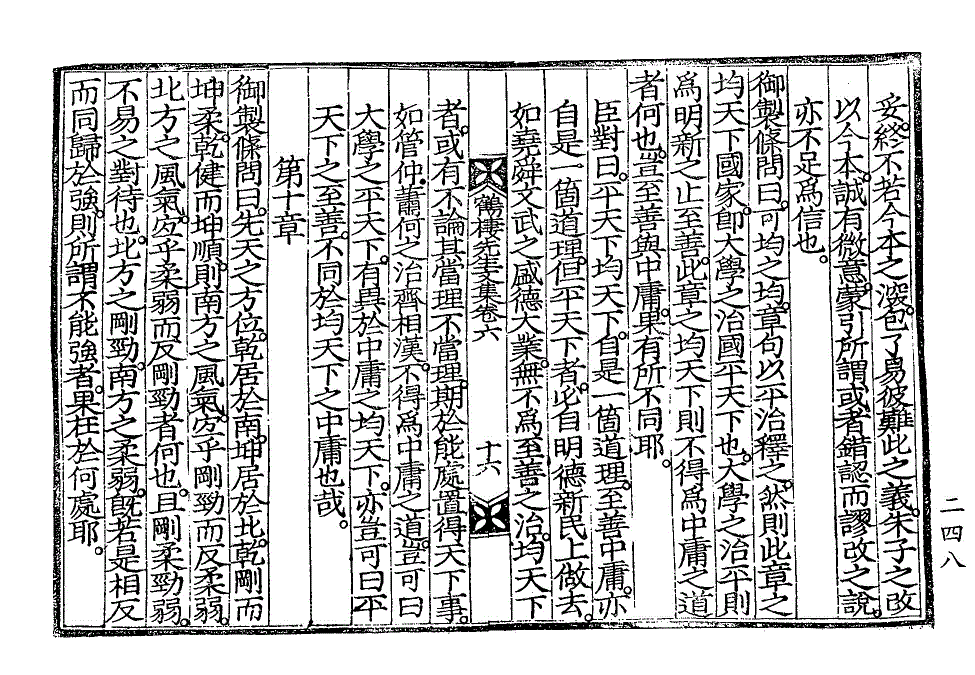 妥。终不若今本之深。包了易彼难此之义。朱子之改以今本。诚有微意。蒙引所谓或者错认而谬改之说。亦不足为信也。
妥。终不若今本之深。包了易彼难此之义。朱子之改以今本。诚有微意。蒙引所谓或者错认而谬改之说。亦不足为信也。御制条问曰。可均之均。章句以平治释之。然则此章之均天下国家。即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也。大学之治平则为明新之止至善。此章之均天下则不得为中庸之道者何也。岂至善与中庸。果有所不同耶。
臣对曰。平天下均天下。自是一个道理。至善中庸。亦自是一个道理。但平天下者。必自明德新民上做去。如尧舜文武之盛德大业。无不为至善之治。均天下者。或有不论其当理不当理。期于能处置得天下事。如管仲,萧何之治齐相汉。不得为中庸之道。岂可曰大学之平天下。有异于中庸之均天下。亦岂可曰平天下之至善。不同于均天下之中庸也哉。
第十章
御制条问曰。先天之方位。乾居于南。坤居于北。乾刚而坤柔。乾健而坤顺。则南方之风气。宜乎刚劲而反柔弱。北方之风气。宜乎柔弱而反刚劲者何也。且刚柔劲弱。不易之对待也。北方之刚劲。南方之柔弱。既若是相反而同归于强。则所谓不能强者。果在于何处耶。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9H 页
 臣对曰。乾刚而坤柔。乾健而坤顺。虽是天地之理也。而体刚者用柔。体顺者用健。南方虽是乾阳之方而其用也柔。则禀是气者。所以为柔弱也。北方虽是阴柔之位而其用也刚。则禀是气者。所以为刚劲也。然此特论其大槩耳。南方岂无果敢之勇。北方岂无含忍之人乎。南北虽有刚柔之别。而其胜人处便可谓之强。彼太柔太弱而不足与论于强者。亦是常理之外。又何居处方所之可论耶。
臣对曰。乾刚而坤柔。乾健而坤顺。虽是天地之理也。而体刚者用柔。体顺者用健。南方虽是乾阳之方而其用也柔。则禀是气者。所以为柔弱也。北方虽是阴柔之位而其用也刚。则禀是气者。所以为刚劲也。然此特论其大槩耳。南方岂无果敢之勇。北方岂无含忍之人乎。南北虽有刚柔之别。而其胜人处便可谓之强。彼太柔太弱而不足与论于强者。亦是常理之外。又何居处方所之可论耶。御制条问曰。此章之言强。与孟子之言养勇。大略相似。南方之强。即孟施舍之勇也。北方之强。即北宫黝之勇也。君子之强。即曾子之勇也。其先叙血气之勇。而后说出义理之勇者。辞意文法。若合符契。思孟之授受。于此亦可见矣。然孟施舍之勇则但谓似于曾子。南方之强则直称君子居之。观于居字似字之别。不无一轩一轾之异者何也。
臣对曰。此章之强。以德行言。邹书之养勇。以浩气体段言。然其辞意文法。大略相似。不胜犹胜。正是宽柔不报。不受万乘。正是死而不厌。反身徇理。守得其要。正是不流不倚不变。 圣问中思孟授受。于此可见之训。明且切矣。若夫孟舍之勇。较诸曾子之勇。说得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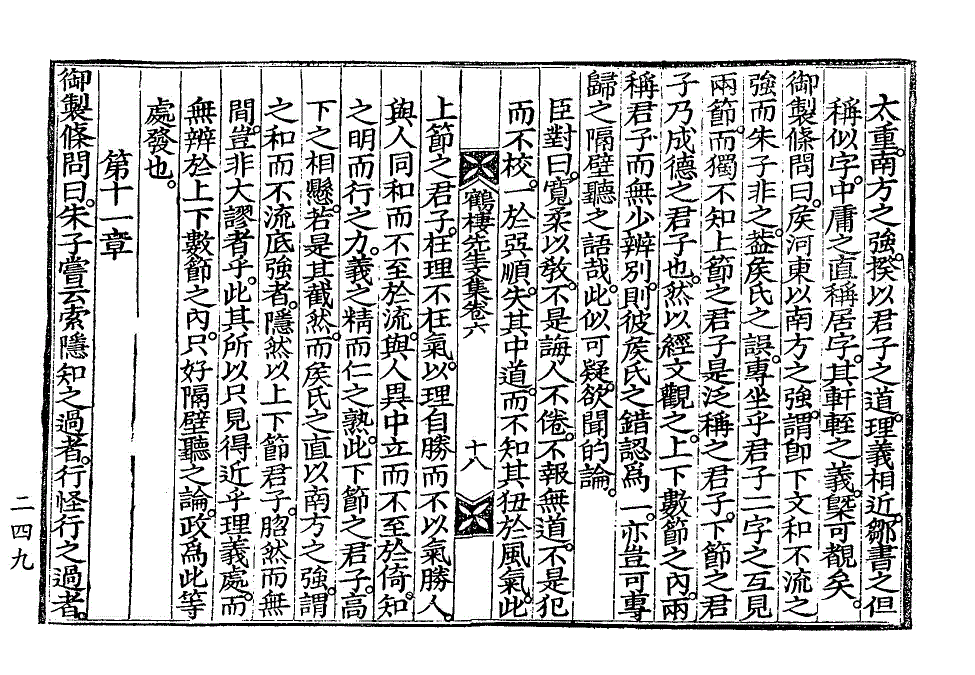 太重。南方之强。揆以君子之道。理义相近。邹书之但称似字。中庸之直称居字。其轩轾之义。槩可睹矣。
太重。南方之强。揆以君子之道。理义相近。邹书之但称似字。中庸之直称居字。其轩轾之义。槩可睹矣。御制条问曰。侯河东以南方之强。谓即下文和不流之强而朱子非之。盖侯氏之误。专坐乎君子二字之互见两节。而独不知上节之君子是泛称之君子。下节之君子乃成德之君子也。然以经文观之。上下数节之内。两称君子而无少辨别。则彼侯氏之错认为一。亦岂可专归之隔壁听之语哉。此似可疑。欲闻的论。
臣对曰。宽柔以教。不是诲人不倦。不报无道。不是犯而不校。一于巽顺。失其中道。而不知其狃于风气。此上节之君子。在理不在气。以理自胜而不以气胜人。与人同和而不至于流。与人异中立而不至于倚。知之明而行之力。义之精而仁之熟。此下节之君子。高下之相悬。若是其截然。而侯氏之直以南方之强。谓之和而不流底强者。隐然以上下节君子。吻然而无间。岂非大谬者乎。此其所以只见得近乎理义处。而无辨于上下数节之内。只好隔壁听之论。政为此等处发也。
第十一章
御制条问曰。朱子尝云索隐知之过者。行怪行之过者。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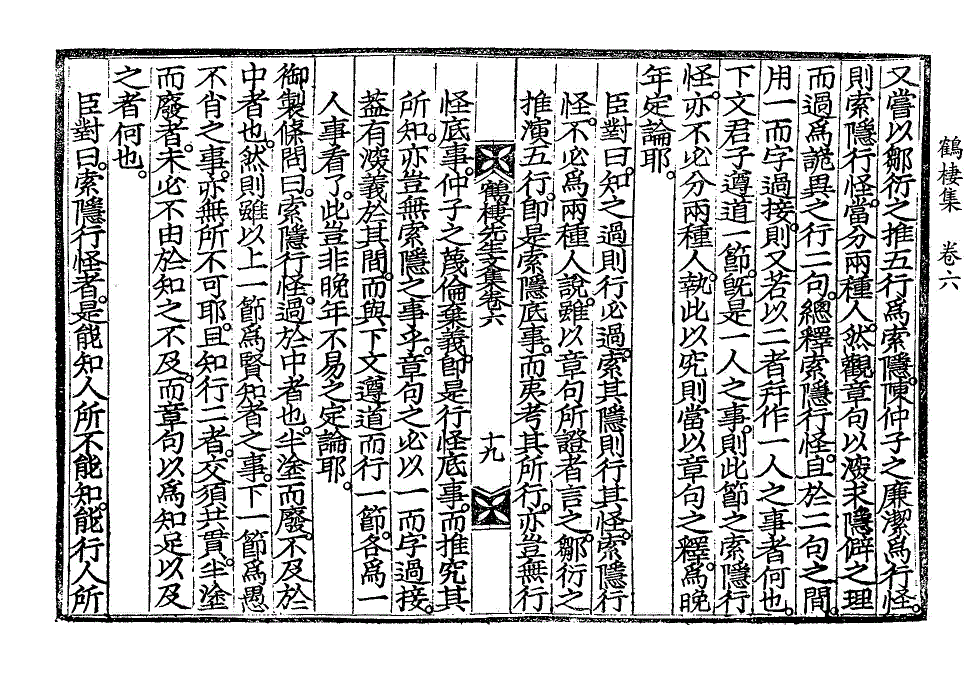 又尝以邹衍之推五行为索隐。陈仲子之廉洁为行怪。则索隐行怪。当分两种人。然观章句以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二句。总释索隐行怪。且于二句之间。用一而字过接。则又若以二者并作一人之事者何也。下文君子遵道一节。既是一人之事。则此节之索隐行怪。亦不必分两种人。执此以究则当以章句之释。为晚年定论耶。
又尝以邹衍之推五行为索隐。陈仲子之廉洁为行怪。则索隐行怪。当分两种人。然观章句以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二句。总释索隐行怪。且于二句之间。用一而字过接。则又若以二者并作一人之事者何也。下文君子遵道一节。既是一人之事。则此节之索隐行怪。亦不必分两种人。执此以究则当以章句之释。为晚年定论耶。臣对曰。知之过则行必过。索其隐则行其怪。索隐行怪。不必为两种人说。虽以章句所證者言之。邹衍之推演五行。即是索隐底事。而夷考其所行。亦岂无行怪底事。仲子之蔑伦弃义。即是行怪底事。而推究其所知。亦岂无索隐之事乎。章句之必以一而字过接。盖有深义于其间。而与下文遵道而行一节。各为一人事看了。此岂非晚年不易之定论耶。
御制条问曰。索隐行怪。过于中者也。半涂而废。不及于中者也。然则虽以上一节为贤知者之事。下一节为愚不肖之事。亦无所不可耶。且知行二者。交须共贯。半涂而废者。未必不由于知之不及。而章句以为知足以及之者何也。
臣对曰。索隐行怪者。是能知人所不能知。能行人所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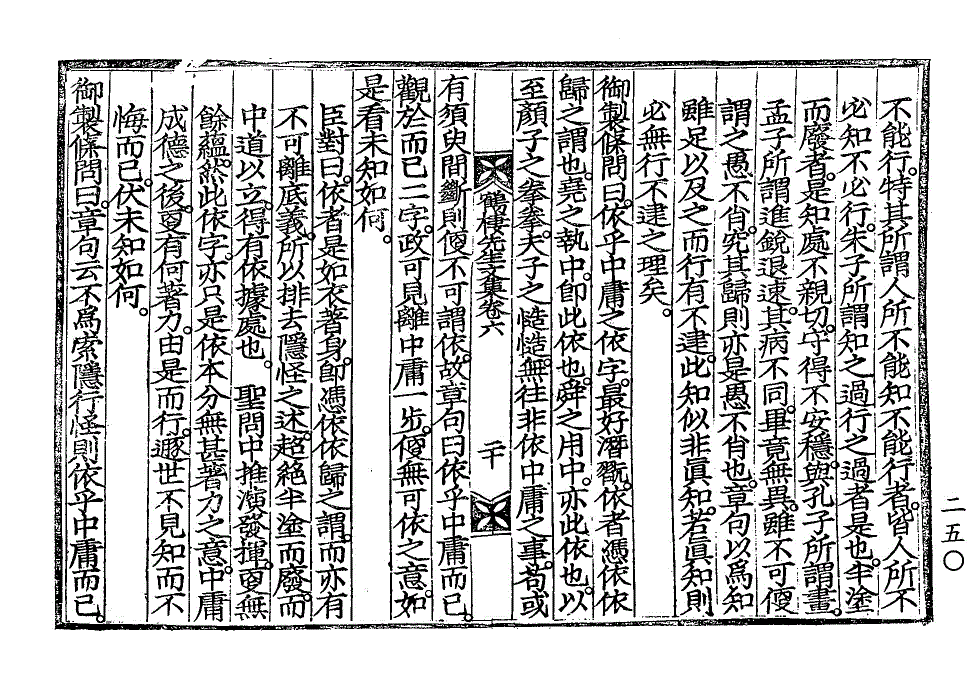 不能行。特其所谓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朱子所谓知之过行之过者是也。半涂而废者。是知处不亲切。守得不安稳。与孔子所谓画。孟子所谓进锐退速。其病不同。毕竟无异。虽不可便谓之愚不肖。究其归则亦是愚不肖也。章句以为知虽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此知似非真知。若真知则必无行不逮之理矣。
不能行。特其所谓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者。皆人所不必知不必行。朱子所谓知之过行之过者是也。半涂而废者。是知处不亲切。守得不安稳。与孔子所谓画。孟子所谓进锐退速。其病不同。毕竟无异。虽不可便谓之愚不肖。究其归则亦是愚不肖也。章句以为知虽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此知似非真知。若真知则必无行不逮之理矣。御制条问曰。依乎中庸之依字。最好潜玩。依者凭依依归之谓也。尧之执中。即此依也。舜之用中。亦此依也。以至颜子之拳拳。夫子之慥慥。无往非依中庸之事。苟或有须臾间断则便不可谓依。故章句曰依乎中庸而已。观于而已二字。政可见离中庸一步。便无可依之意。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对曰。依者是如衣著身。即凭依依归之谓。而亦有不可离底义。所以排去隐怪之述。超绝半涂而废。而中道以立。得有依据处也。 圣问中推演发挥。更无馀蕴。然此依字。亦只是依本分无甚著力之意。中庸成德之后。更有何著力。由是而行。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而已。伏未知如何。
御制条问曰。章句云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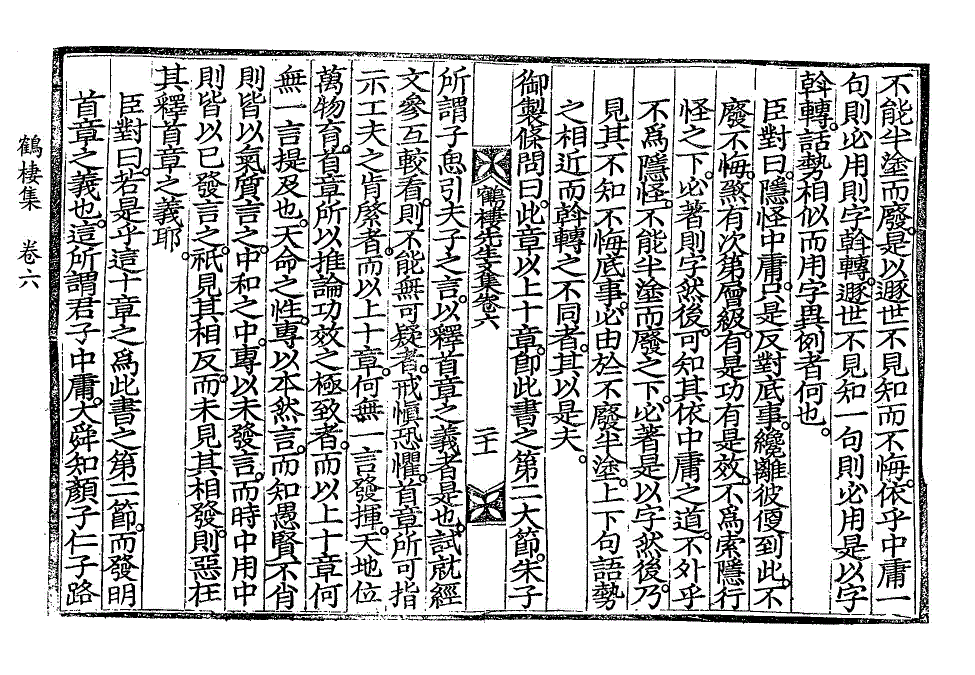 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依乎中庸一句则必用则字斡转。遁世不见知一句则必用是以字斡转。话势相似而用字异例者何也。
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依乎中庸一句则必用则字斡转。遁世不见知一句则必用是以字斡转。话势相似而用字异例者何也。臣对曰。隐怪中庸。只是反对底事。才离彼便到此。不废不悔。煞有次第层级。有是功有是效。不为索隐行怪之下。必著则字然后。可知其依中庸之道。不外乎不为隐怪。不能半涂而废之下。必著是以字然后。乃见其不知不悔底事。必由于不废半涂。上下句语势之相近而斡转之不同者。其以是夫。
御制条问曰。此章以上十章。即此书之第二大节。朱子所谓子思引夫子之言。以释首章之义者是也。试就经文参互较看。则不能无可疑者。戒慎恐惧。首章所可指示工夫之肯綮者。而以上十章。何无一言发挥。天地位万物育。首章所以推论功效之极致者。而以上十章何无一言提及也。天命之性。专以本然言。而知愚贤不肖则皆以气质言之。中和之中。专以未发言。而时中用中则皆以已发言之。祇见其相反。而未见其相发。则恶在其释首章之义耶。
臣对曰。若是乎这十章之为此书之第二节。而发明首章之义也。这所谓君子中庸。大舜知颜子仁子路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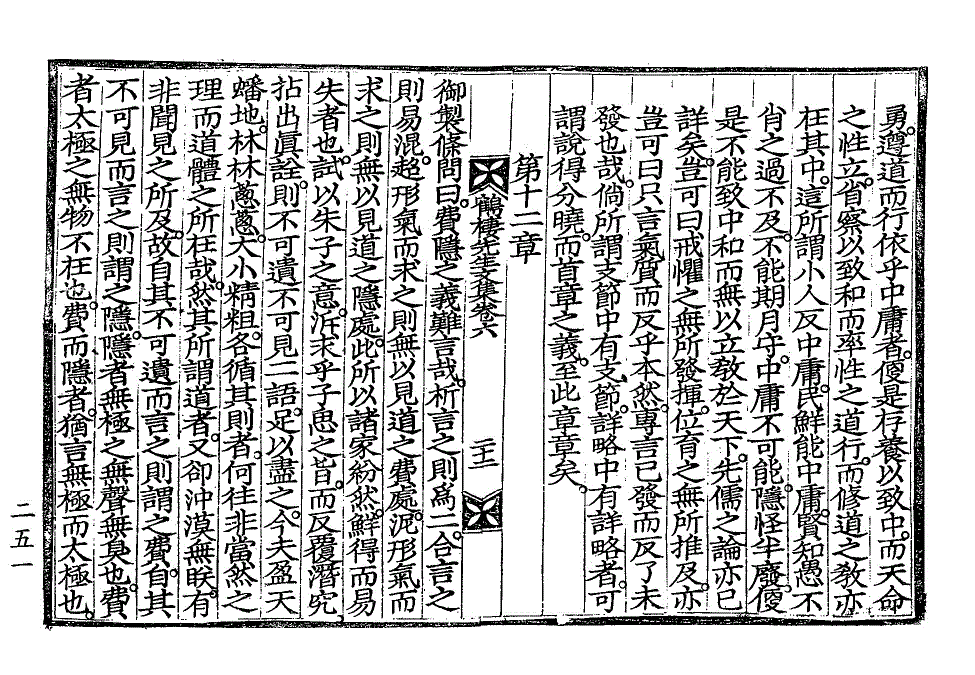 勇。遵道而行依乎中庸者。便是存养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这所谓小人反中庸。民鲜能中庸。贤知愚不肖之过不及。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隐怪半废。便是不能致中和而无以立教于天下。先儒之论亦已详矣。岂可曰戒惧之无所发挥。位育之无所推及。亦岂可曰只言气质而反乎本然。专言已发而反了未发也哉。倘所谓支节中有支节。详略中有详略者。可谓说得分晓。而首章之义。至此章章矣。
勇。遵道而行依乎中庸者。便是存养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这所谓小人反中庸。民鲜能中庸。贤知愚不肖之过不及。不能期月守。中庸不可能。隐怪半废。便是不能致中和而无以立教于天下。先儒之论亦已详矣。岂可曰戒惧之无所发挥。位育之无所推及。亦岂可曰只言气质而反乎本然。专言已发而反了未发也哉。倘所谓支节中有支节。详略中有详略者。可谓说得分晓。而首章之义。至此章章矣。第十二章
御制条问曰。费隐之义难言哉。析言之则为二。合言之则易混。超形气而求之则无以见道之费处。泥形气而求之则无以见道之隐处。此所以诸家纷然。鲜得而易失者也。试以朱子之意。溯求乎子思之旨。而反覆潜究。拈出真诠。则不可遗不可见二语。足以尽之。今夫盈天蟠地。林林葱葱。大小精粗。各循其则者。何往非当然之理而道体之所在哉。然其所谓道者。又却冲漠无眹。有非闻见之所及。故自其不可遗而言之则谓之费。自其不可见而言之则谓之隐。隐者无极之无声无臭也。费者太极之无物不在也。费而隐者。犹言无极而太极也。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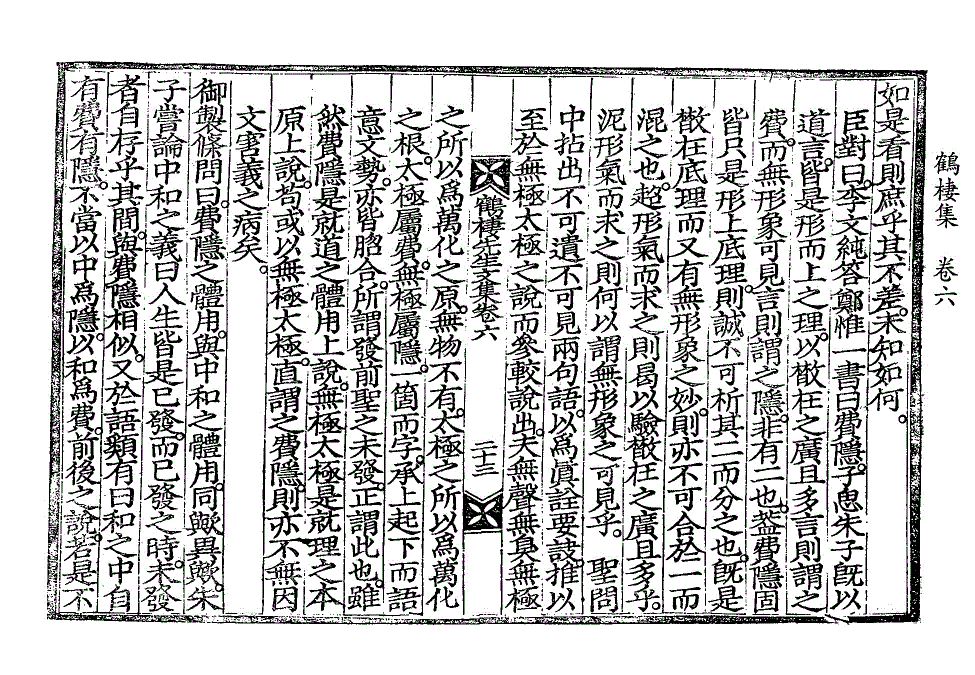 如是看则庶乎其不差。未知如何。
如是看则庶乎其不差。未知如何。臣对曰。李文纯答郑惟一书曰费隐。子思朱子既以道言。皆是形而上之理。以散在之广且多言则谓之费。而无形象可见言则谓之隐。非有二也。盖费隐固皆只是形上底理。则诚不可析其二而分之也。既是散在底理而又有无形象之妙。则亦不可合于一而混之也。超形气而求之则曷以验散在之广且多乎。泥形气而求之则何以谓无形象之可见乎。 圣问中拈出不可遗不可见两句语。以为真诠要诀。推以至于无极太极之说而参较说出。夫无声无臭无极之所以为万化之原。无物不有。太极之所以为万化之根。太极属费。无极属隐。一个而字。承上起下而语意文势。亦皆吻合。所谓发前圣之未发。正谓此也。虽然费隐是就道之体用上说。无极太极是就理之本原上说。苟或以无极太极。直谓之费隐。则亦不无因文害义之病矣。
御制条问曰。费隐之体用。与中和之体用。同欤异欤。朱子尝论中和之义曰人生皆是已发。而已发之时。未发者自存乎其间。与费隐相似。又于语类有曰和之中自有费有隐。不当以中为隐。以和为费。前后之说。若是不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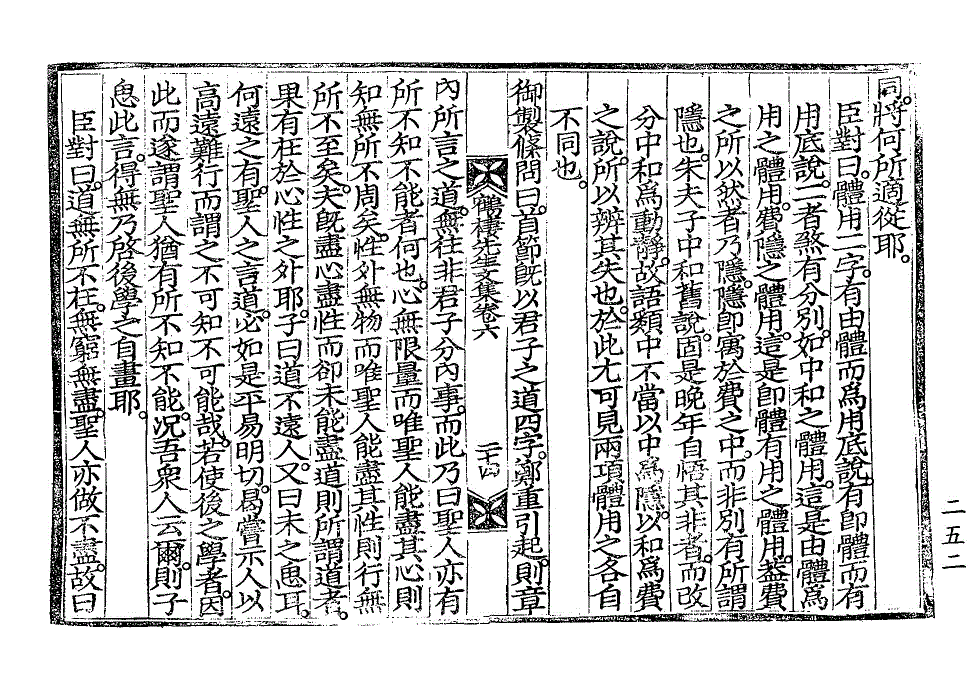 同。将何所适从耶。
同。将何所适从耶。臣对曰。体用二字。有由体而为用底说。有即体而有用底说。二者煞有分别。如中和之体用。这是由体为用之体用。费隐之体用。这是即体有用之体用。盖费之所以然者乃隐。隐即寓于费之中。而非别有所谓隐也。朱夫子中和旧说。固是晚年自悟其非者。而改分中和为动静。故语类中不当以中为隐。以和为费之说。所以辨其失也。于此尤可见两项体用之各自不同也。
御制条问曰。首节既以君子之道四字。郑重引起。则章内所言之道。无往非君子分内事。而此乃曰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何也。心无限量而唯圣人能尽其心则知无所不周矣。性外无物而唯圣人能尽其性则行无所不至矣。夫既尽心尽性而却未能尽道则所谓道者。果有在于心性之外耶。子曰道不远人。又曰未之思耳。何远之有。圣人之言道。必如是平易明切。曷尝示人以高远难行而谓之不可知不可能哉。若使后之学者。因此而遂谓圣人犹有所不知不能。况吾众人云尔。则子思此言。得无乃启后学之自画耶。
臣对曰。道无所不在。无穷无尽。圣人亦做不尽。故曰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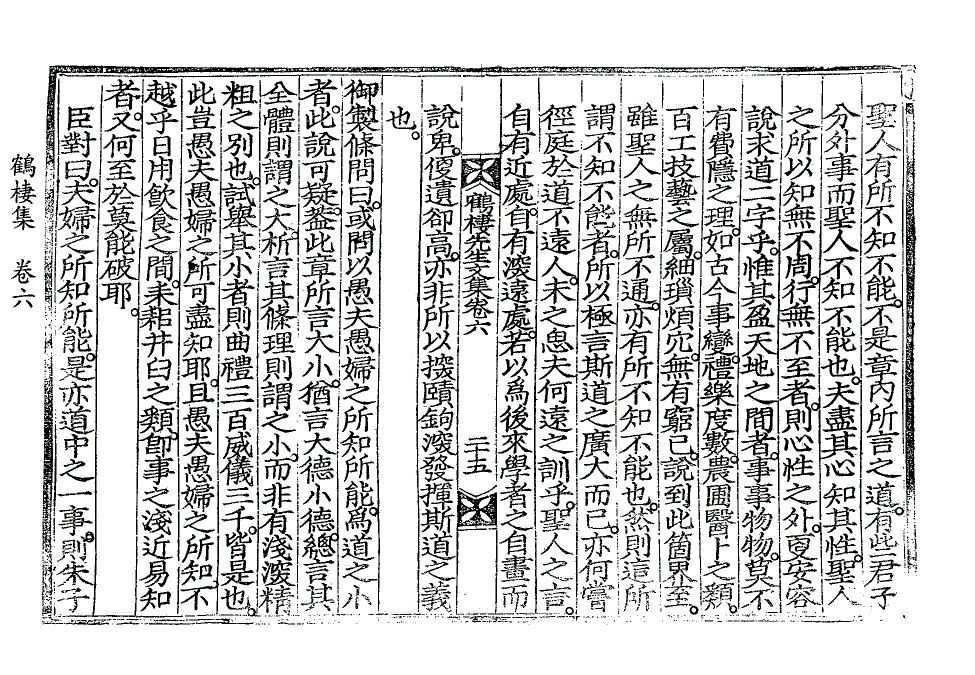 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不是章内所言之道。有些君子分外事而圣人不知不能也。夫尽其心知其性。圣人之所以知无不周。行无不至者。则心性之外。更安容说求道二字乎。惟其盈天地之间者。事事物物。莫不有费隐之理。如古今事变。礼乐度数。农圃医卜之类。百工技艺之属。细琐烦冗。无有穷已。说到此个界至。虽圣人之无所不通。亦有所不知不能也。然则这所谓不知不能者。所以极言斯道之广大而已。亦何尝径庭于道不远人。未之思夫何远之训乎。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远处。若以为后来学者之自画而说卑。便遗却高。亦非所以探赜钩深发挥斯道之义也。
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不是章内所言之道。有些君子分外事而圣人不知不能也。夫尽其心知其性。圣人之所以知无不周。行无不至者。则心性之外。更安容说求道二字乎。惟其盈天地之间者。事事物物。莫不有费隐之理。如古今事变。礼乐度数。农圃医卜之类。百工技艺之属。细琐烦冗。无有穷已。说到此个界至。虽圣人之无所不通。亦有所不知不能也。然则这所谓不知不能者。所以极言斯道之广大而已。亦何尝径庭于道不远人。未之思夫何远之训乎。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远处。若以为后来学者之自画而说卑。便遗却高。亦非所以探赜钩深发挥斯道之义也。御制条问曰。或问以愚夫愚妇之所知所能。为道之小者。此说可疑。盖此章所言大小。犹言大德小德。总言其全体则谓之大。析言其条理则谓之小。而非有浅深精粗之别也。试举其小者则曲礼三百威仪三千。皆是也。此岂愚夫愚妇之所可尽知耶。且愚夫愚妇之所知。不越乎日用饮食之间。耒耜井臼之类。即事之浅近易知者。又何至于莫能破耶。
臣对曰。夫妇之所知所能。是亦道中之一事。则朱子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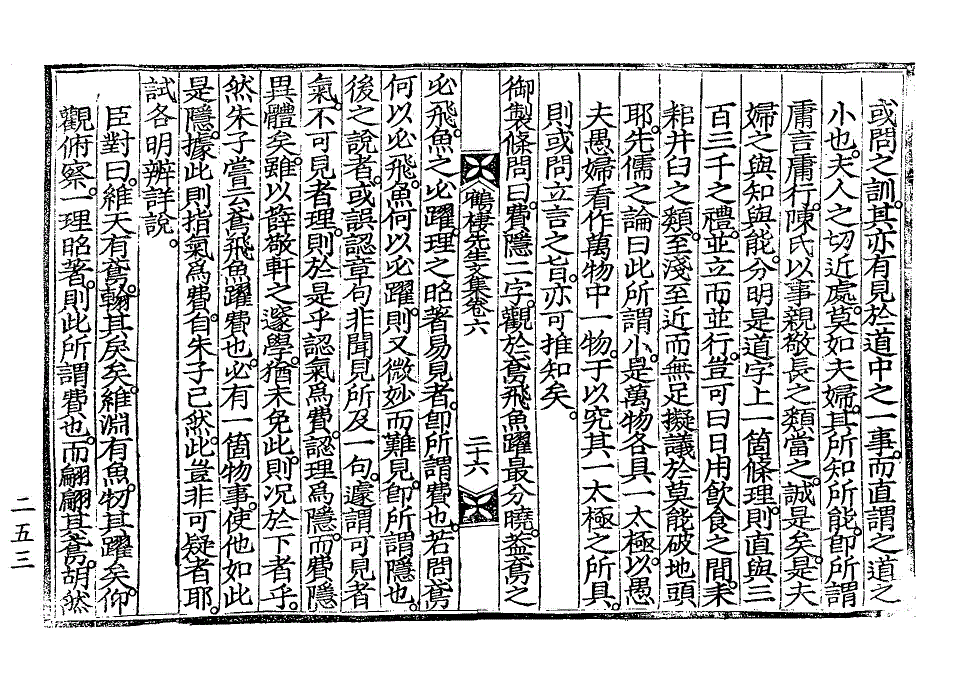 或问之训。其亦有见于道中之一事。而直谓之道之小也。夫人之切近处。莫如夫妇。其所知所能。即所谓庸言庸行。陈氏以事亲敬长之类当之。诚是矣。是夫妇之与知与能。分明是道字上一个条理。则直与三百三千之礼。并立而并行。岂可曰日用饮食之间。耒耜井臼之类。至浅至近而无足拟议于莫能破地头耶。先儒之论曰此所谓小。是万物各具一太极。以愚夫愚妇看作万物中一物。于以究其一太极之所具。则或问立言之旨。亦可推知矣。
或问之训。其亦有见于道中之一事。而直谓之道之小也。夫人之切近处。莫如夫妇。其所知所能。即所谓庸言庸行。陈氏以事亲敬长之类当之。诚是矣。是夫妇之与知与能。分明是道字上一个条理。则直与三百三千之礼。并立而并行。岂可曰日用饮食之间。耒耜井臼之类。至浅至近而无足拟议于莫能破地头耶。先儒之论曰此所谓小。是万物各具一太极。以愚夫愚妇看作万物中一物。于以究其一太极之所具。则或问立言之旨。亦可推知矣。御制条问曰。费隐二字。观于鸢飞鱼跃最分晓。盖鸢之必飞。鱼之必跃。理之昭著易见者。即所谓费也。若问鸢何以必飞。鱼何以必跃。则又微妙而难见。即所谓隐也。后之说者。或误认章句非闻见所及一句。遽谓可见者气。不可见者理。则于是乎认气为费。认理为隐。而费隐异体矣。虽以薛敬轩之邃学。犹未免此。则况于下者乎。然朱子尝云鸢飞鱼跃费也。必有一个物事。使他如此是隐。据此则指气为费。自朱子已然。此岂非可疑者耶。试各明辨详说。
臣对曰。维天有鸢。翰其戾矣。维渊有鱼。牣其跃矣。仰观俯察。一理昭著。则此所谓费也。而翩翩其鸢。胡然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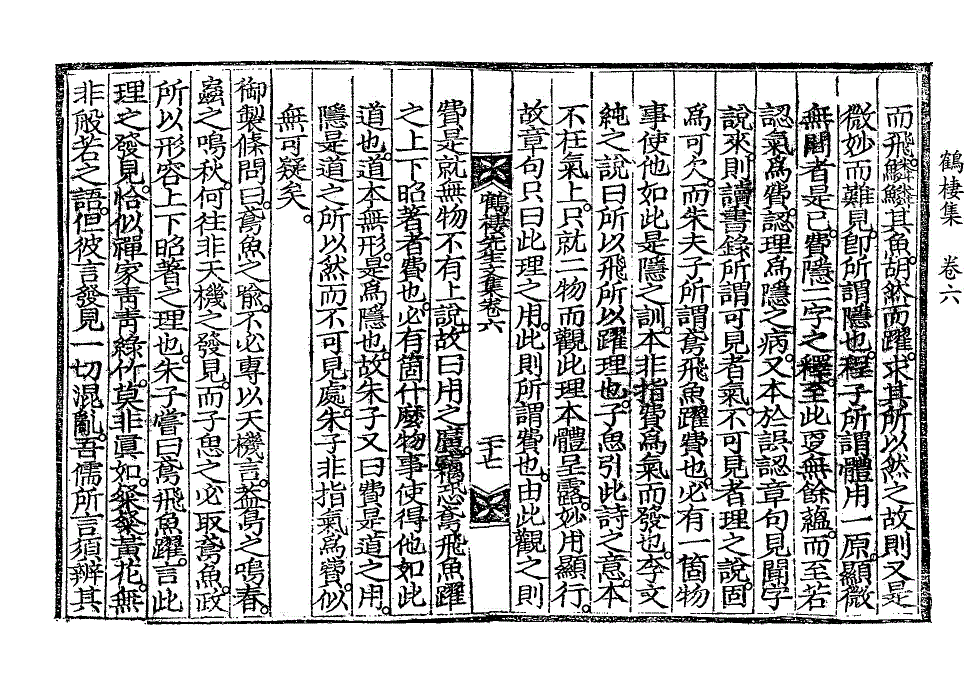 而飞。鳞鳞其鱼。胡然而跃。求其所以然之故则又是微妙而难见。即所谓隐也。程子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是已。费隐一字之释。至此更无馀蕴。而至若认气为费。认理为隐之病。又本于误认章句见闻字说来。则读书录所谓可见者气。不可见者理之说。固为可欠。而朱夫子所谓鸢飞鱼跃费也。必有一个物事使他如此是隐之训。本非指费为气而发也。李文纯之说曰所以飞所以跃理也。子思引此诗之意。本不在气上。只就二物而观此理本体呈露。妙用显行。故章句只曰此理之用。此则所谓费也。由此观之则费是就无物不有上说。故曰用之广。窃恐鸢飞鱼跃之上下昭著者费也。必有个什么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道本无形。是为隐也。故朱子又曰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朱子非指气为费。似无可疑矣。
而飞。鳞鳞其鱼。胡然而跃。求其所以然之故则又是微妙而难见。即所谓隐也。程子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是已。费隐一字之释。至此更无馀蕴。而至若认气为费。认理为隐之病。又本于误认章句见闻字说来。则读书录所谓可见者气。不可见者理之说。固为可欠。而朱夫子所谓鸢飞鱼跃费也。必有一个物事使他如此是隐之训。本非指费为气而发也。李文纯之说曰所以飞所以跃理也。子思引此诗之意。本不在气上。只就二物而观此理本体呈露。妙用显行。故章句只曰此理之用。此则所谓费也。由此观之则费是就无物不有上说。故曰用之广。窃恐鸢飞鱼跃之上下昭著者费也。必有个什么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道本无形。是为隐也。故朱子又曰费是道之用。隐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见处。朱子非指气为费。似无可疑矣。御制条问曰。鸢鱼之喻。不必专以天机言。盖鸟之鸣春。虫之鸣秋。何往非天机之发见。而子思之必取鸢鱼。政所以形容上下昭著之理也。朱子尝曰鸢飞鱼跃。言此理之发见。恰似禅家青青绿竹。莫非真如。粲粲黄花。无非般若之语。但彼言发见一切混乱。吾儒所言须辨其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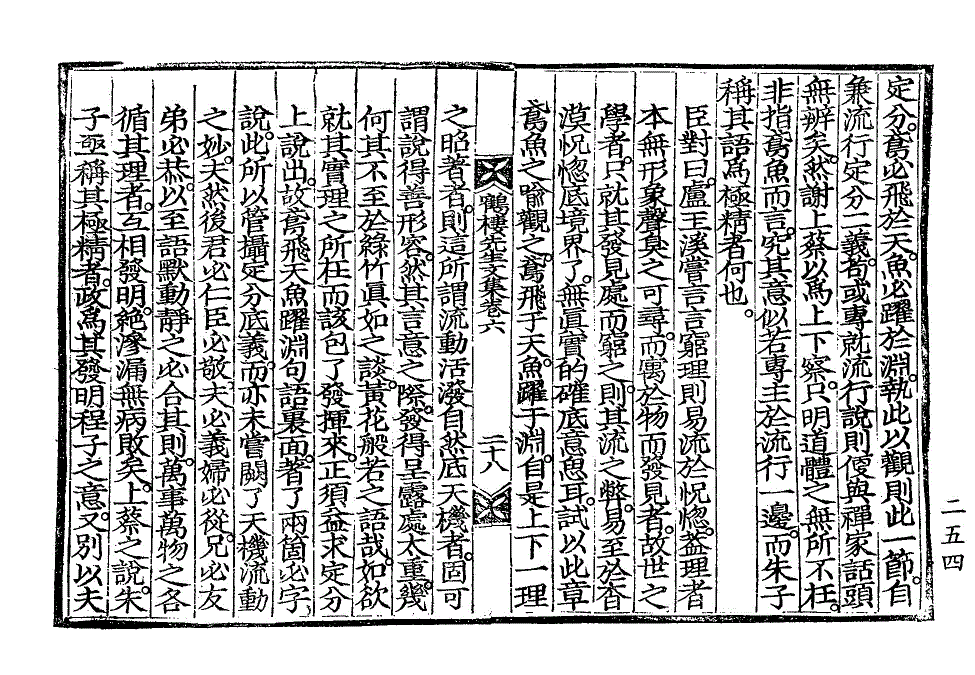 定分。鸢必飞于天。鱼必跃于渊。执此以观则此一节。自兼流行定分二义。苟或专就流行说则便与禅家话头无辨矣。然谢上蔡以为上下察。只明道体之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究其意似若专主于流行一边。而朱子称其语为极精者何也。
定分。鸢必飞于天。鱼必跃于渊。执此以观则此一节。自兼流行定分二义。苟或专就流行说则便与禅家话头无辨矣。然谢上蔡以为上下察。只明道体之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究其意似若专主于流行一边。而朱子称其语为极精者何也。臣对曰。卢玉溪尝言言穷理则易流于恍惚。盖理者本无形象声臭之可寻。而寓于物而发见者。故世之学者。只就其发见处而穷之。则其流之弊。易至于杳漠恍惚底境界了。无真实的确底意思耳。试以此章鸢鱼之喻观之。鸢飞于天。鱼跃于渊。自是上下一理之昭著者。则这所谓流动活泼自然底天机者。固可谓说得善形容。然其言意之际。发得呈露处太重。几何其不至于绿竹真如之谈。黄花般若之语哉。如欲就其实理之所在而该包了发挥来。正须益求定分上说出。故鸢飞天鱼跃渊句语里面。著了两个必字说。此所以管摄定分底义。而亦未尝阙了天机流动之妙。夫然后君必仁臣必敬。夫必义妇必从。兄必友弟必恭。以至语默动静之必合其则。万事万物之各循其理者。互相发明。绝渗漏无病败矣。上蔡之说。朱子亟称其极精者。政为其发明程子之意。又别以夫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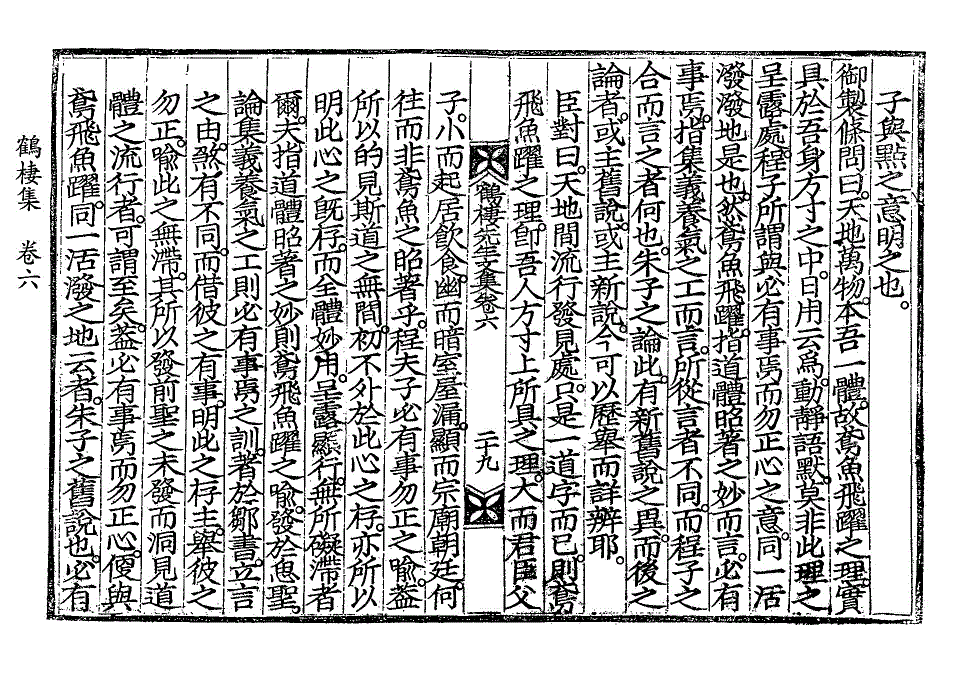 子与点之意明之也。
子与点之意明之也。御制条问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故鸢鱼飞跃之理。实具于吾身方寸之中。日用云为。动静语默。莫非此理之呈露处。程子所谓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一活泼泼地是也。然鸢鱼飞跃。指道体昭著之妙而言。必有事焉。指集义养气之工而言。所从言者不同。而程子之合而言之者何也。朱子之论此。有新旧说之异。而后之论者。或主旧说。或主新说。今可以历举而详辨耶。
臣对曰。天地间流行发见处。只是一道字而已。则鸢飞鱼跃之理。即吾人方寸上所具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饮食。幽而暗室屋漏。显而宗庙朝廷。何往而非鸢鱼之昭著乎。程夫子必有事勿正之喻。盖所以的见斯道之无间。初不外于此心之存。亦所以明此心之既存。而全体妙用。呈露显行。无所碍滞者尔。夫指道体昭著之妙则鸢飞鱼跃之喻。发于思圣。论集义养气之工则必有事焉之训。著于邹书。立言之由。煞有不同。而借彼之有事。明此之存主。举彼之勿正。喻此之无滞。其所以发前圣之未发而洞见道体之流行者。可谓至矣。盖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便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之地云者。朱子之旧说也。必有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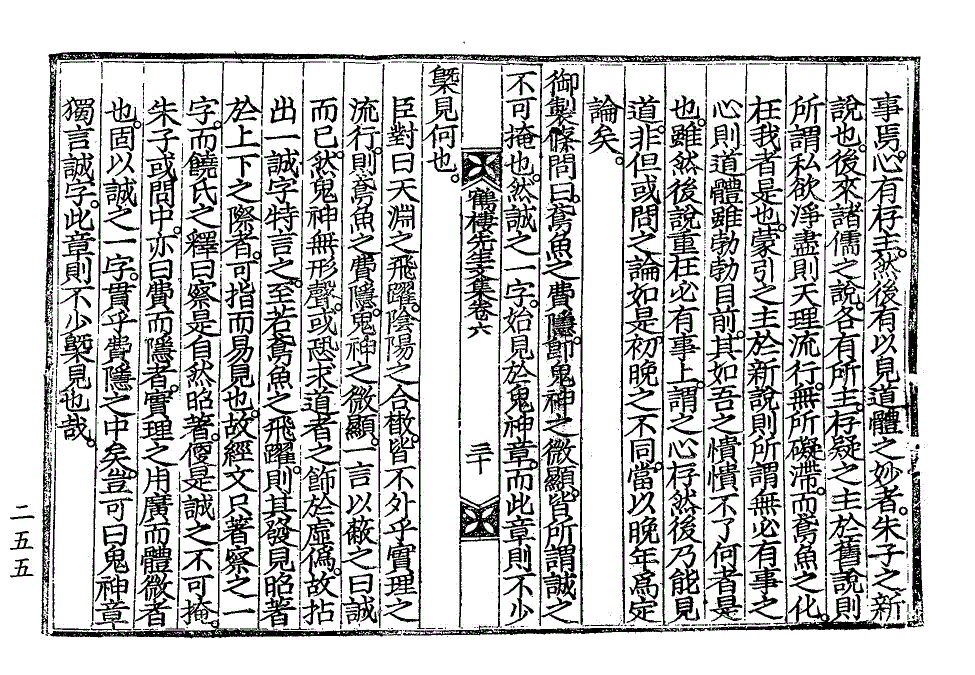 事焉。心有存主。然后有以见道体之妙者。朱子之新说也。后来诸儒之说。各有所主。存疑之主于旧说则所谓私欲净尽则天理流行。无所碍滞。而鸢鱼之化。在我者是也。蒙引之主于新说则所谓无必有事之心则道体虽勃勃目前。其如吾之愦愦不了何者是也。虽然后说重在必有事上。谓之心存然后乃能见道。非但或问之论如是。初晚之不同。当以晚年为定论矣。
事焉。心有存主。然后有以见道体之妙者。朱子之新说也。后来诸儒之说。各有所主。存疑之主于旧说则所谓私欲净尽则天理流行。无所碍滞。而鸢鱼之化。在我者是也。蒙引之主于新说则所谓无必有事之心则道体虽勃勃目前。其如吾之愦愦不了何者是也。虽然后说重在必有事上。谓之心存然后乃能见道。非但或问之论如是。初晚之不同。当以晚年为定论矣。御制条问曰。鸢鱼之费隐。即鬼神之微显。皆所谓诚之不可掩也。然诚之一字。始见于鬼神章。而此章则不少槩见何也。
臣对曰天渊之飞跃。阴阳之合散。皆不外乎实理之流行。则鸢鱼之费隐。鬼神之微显。一言以蔽之曰诚而已。然鬼神无形声。或恐求道者之饰于虚伪。故拈出一诚字特言之。至若鸢鱼之飞跃。则其发见昭著于上下之际者。可指而易见也。故经文只著察之一字。而饶氏之释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诚之不可掩。朱子或问中。亦曰费而隐者。实理之用广而体微者也。固以诚之一字。贯乎费隐之中矣。岂可曰鬼神章独言诚字。此章则不少槩见也哉。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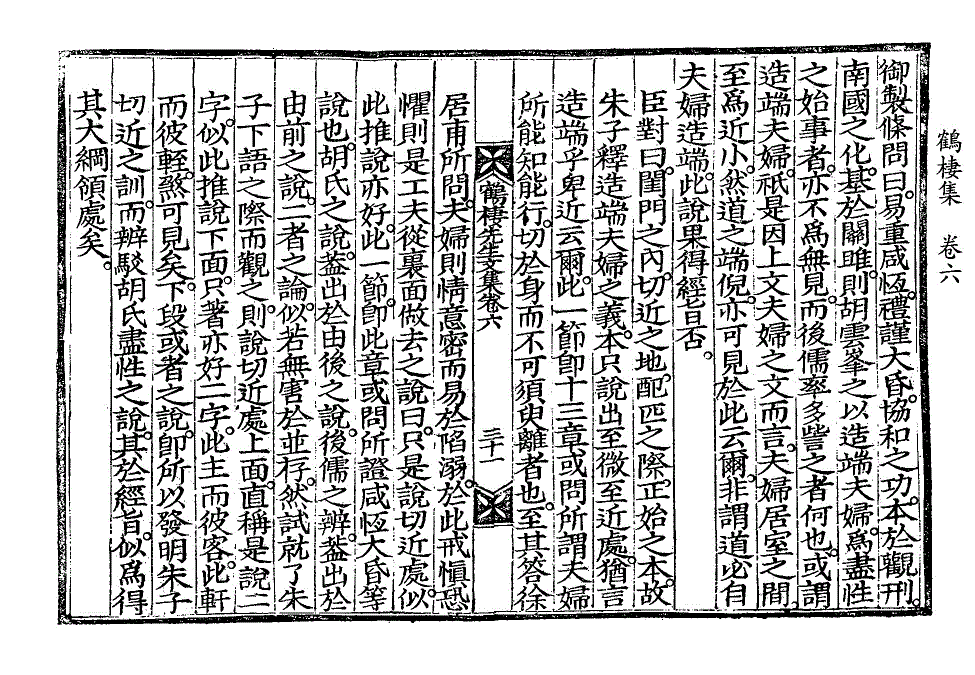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易重咸恒。礼谨大昏。协和之功。本于观刑。南国之化。基于关雎。则胡云峰之以造端夫妇。为尽性之始事者。亦不为无见。而后儒率多訾之者何也。或谓造端夫妇。祇是因上文夫妇之文而言。夫妇居室之间。至为近小。然道之端倪。亦可见于此云尔。非谓道必自夫妇造端。此说果得经旨否。
御制条问曰。易重咸恒。礼谨大昏。协和之功。本于观刑。南国之化。基于关雎。则胡云峰之以造端夫妇。为尽性之始事者。亦不为无见。而后儒率多訾之者何也。或谓造端夫妇。祇是因上文夫妇之文而言。夫妇居室之间。至为近小。然道之端倪。亦可见于此云尔。非谓道必自夫妇造端。此说果得经旨否。臣对曰。闺门之内。切近之地。配匹之际。正始之本。故朱子释造端夫妇之义。本只说出至微至近处。犹言造端乎卑近云尔。此一节即十三章或问所谓夫妇所能知能行。切于身而不可须臾离者也。至其答徐居甫所问。夫妇则情意密而易于陷溺。于此戒慎恐惧则是工夫从里面做去之说曰。只是说切近处。似此推说亦好。此一节。即此章或问所證咸恒大昏等说也。胡氏之说。盖出于由后之说。后儒之辨。盖出于由前之说。二者之论。似若无害于并存。然试就了朱子下语之际而观之。则说切近处上面。直称是说二字。似此推说下面。只著亦好二字。此主而彼客。此轩而彼轾。煞可见矣。下段或者之说。即所以发明朱子切近之训。而辨驳胡氏尽性之说。其于经旨。似为得其大纲领处矣。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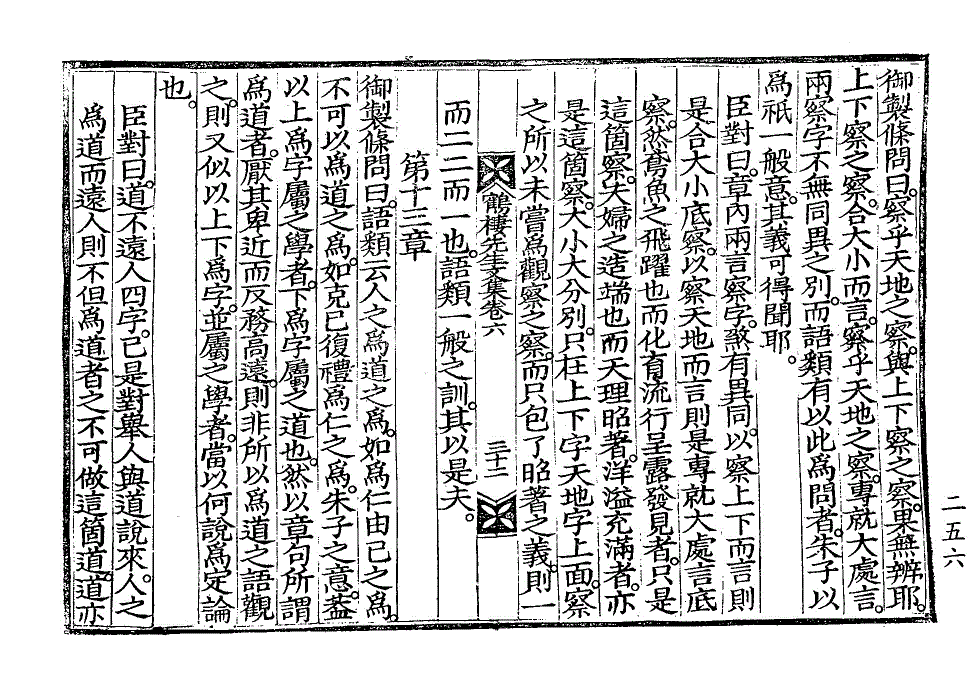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察乎天地之察。与上下察之察。果无辨耶。上下察之察。合大小而言。察乎天地之察。专就大处言。两察字不无同异之别。而语类有以此为问者。朱子以为祇一般意。其义可得闻耶。
御制条问曰。察乎天地之察。与上下察之察。果无辨耶。上下察之察。合大小而言。察乎天地之察。专就大处言。两察字不无同异之别。而语类有以此为问者。朱子以为祇一般意。其义可得闻耶。臣对曰。章内两言察字。煞有异同。以察上下而言则是合大小底察。以察天地而言则是专就大处言底察。然鸢鱼之飞跃也而化育流行呈露发见者。只是这个察。夫妇之造端也而天理昭著。洋溢充满者。亦是这个察。大小大分别。只在上下字天地字上面。察之所以未尝为观察之察。而只包了昭著之义。则一而二二而一也。语类一般之训。其以是夫。
第十三章
御制条问曰。语类云人之为道之为。如为仁由己之为。不可以为道之为。如克己复礼为仁之为。朱子之意。盖以上为字属之学者。下为字属之道也。然以章句所谓为道者。厌其卑近而反务高远。则非所以为道之语观之。则又似以上下为字。并属之学者。当以何说为定论也。
臣对曰。道不远人四字。已是对举人与道说来。人之为道而远人则不但为道者之不可做这个道。道亦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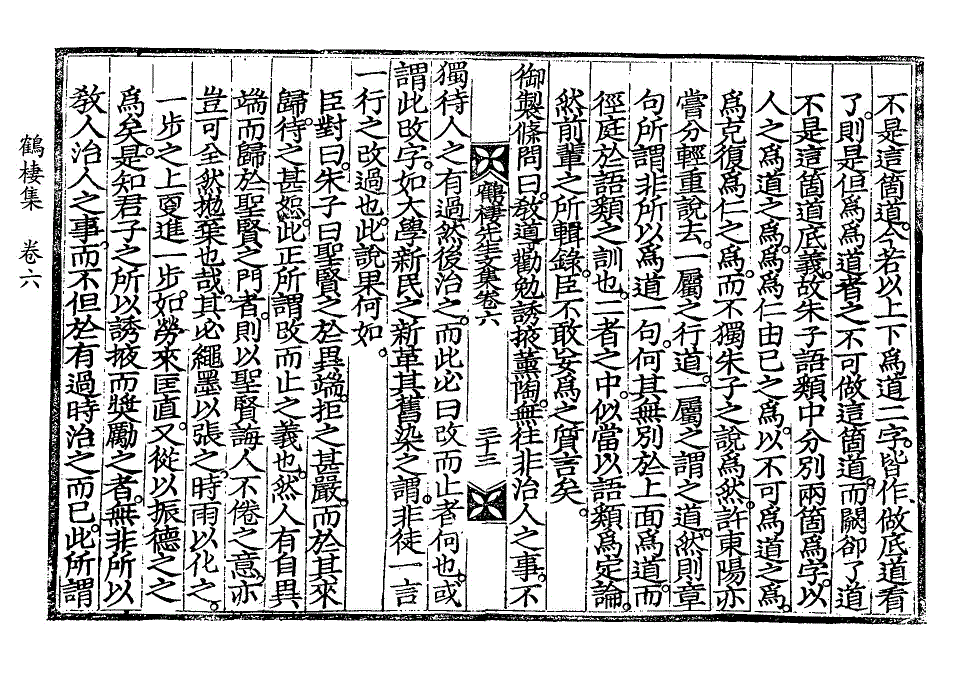 不是这个道。今若以上下为道二字。皆作做底道看了。则是但为为道者之不可做这个道。而阙却了道不是这个道底义。故朱子语类中分别两个为字。以人之为道之为。为为仁由己之为。以不可为道之为。为克复为仁之为。而不独朱子之说为然。许东阳亦尝分轻重说去。一属之行道。一属之谓之道。然则章句所谓非所以为道一句。何其无别于上面为道。而径庭于语类之训也。二者之中。似当以语类为定论。然前辈之所辑录。臣不敢妄为之质言矣。
不是这个道。今若以上下为道二字。皆作做底道看了。则是但为为道者之不可做这个道。而阙却了道不是这个道底义。故朱子语类中分别两个为字。以人之为道之为。为为仁由己之为。以不可为道之为。为克复为仁之为。而不独朱子之说为然。许东阳亦尝分轻重说去。一属之行道。一属之谓之道。然则章句所谓非所以为道一句。何其无别于上面为道。而径庭于语类之训也。二者之中。似当以语类为定论。然前辈之所辑录。臣不敢妄为之质言矣。御制条问曰。教导劝勉诱掖薰陶。无往非治人之事。不独待人之有过然后治之。而此必曰改而止者何也。或谓此改字。如大学新民之新革其旧染之谓。非徒一言一行之改过也。此说果何如。
臣对曰。朱子曰圣贤之于异端。拒之甚严。而于其来归。待之甚恕。此正所谓改而止之义也。然人有自异端而归于圣贤之门者。则以圣贤诲人不倦之意。亦岂可全然抛弃也哉。其必绳墨以张之。时雨以化之。一步之上更进一步。如劳来匡直。又从以振德之之为矣。是知君子之所以诱掖而奖励之者。无非所以教人治人之事。而不但于有过时治之而已。此所谓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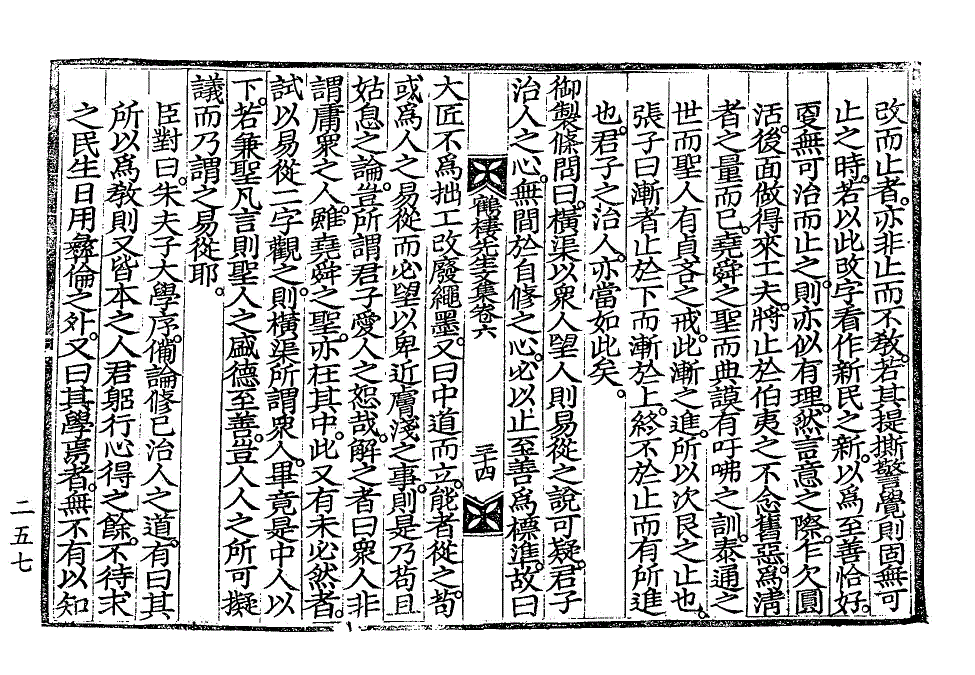 改而止者。亦非止而不教。若其提撕警觉则固无可止之时。若以此改字看作新民之新。以为至善恰好。更无可治而止之。则亦似有理。然言意之际。乍欠圆活。后面做得来工夫。将止于伯夷之不念旧恶。为清者之量而已。尧舜之圣而典谟有吁咈之训。泰通之世而圣人有贞吝之戒。此渐之进。所以次艮之止也。张子曰渐者止于下而渐于上。终不于止而有所进也。君子之治人。亦当如此矣。
改而止者。亦非止而不教。若其提撕警觉则固无可止之时。若以此改字看作新民之新。以为至善恰好。更无可治而止之。则亦似有理。然言意之际。乍欠圆活。后面做得来工夫。将止于伯夷之不念旧恶。为清者之量而已。尧舜之圣而典谟有吁咈之训。泰通之世而圣人有贞吝之戒。此渐之进。所以次艮之止也。张子曰渐者止于下而渐于上。终不于止而有所进也。君子之治人。亦当如此矣。御制条问曰。横渠以众人望人则易从之说可疑。君子治人之心。无间于自修之心。必以止至善为标准。故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又曰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苟或为人之易从而必望以卑近肤浅之事。则是乃苟且姑息之论。岂所谓君子爱人之恕哉。解之者曰众人非谓庸众之人。虽尧舜之圣。亦在其中。此又有未必然者。试以易从二字观之。则横渠所谓众人。毕竟是中人以下。若兼圣凡言则圣人之盛德至善。岂人人之所可拟议而乃谓之易从耶。
臣对曰。朱夫子大学序。备论修己治人之道。有曰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馀。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又曰。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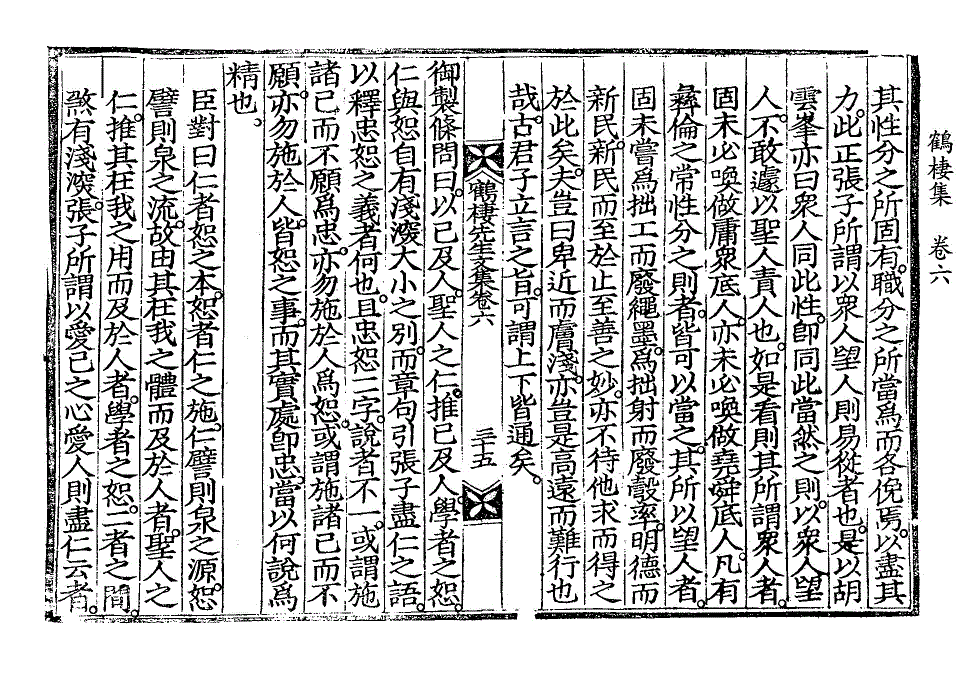 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正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者也。是以胡云峰亦曰众人同此性。即同此当然之则。以众人望人。不敢遽以圣人责人也。如是看则其所谓众人者。固未必唤做庸众底人。亦未必唤做尧舜底人。凡有彝伦之常性分之则者。皆可以当之。其所以望人者。固未尝为拙工而废绳墨。为拙射而废彀率。明德而新民。新民而至于止至善之妙。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夫岂曰卑近而肤浅。亦岂是高远而难行也哉。古君子立言之旨。可谓上下皆通矣。
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正张子所谓以众人望人则易从者也。是以胡云峰亦曰众人同此性。即同此当然之则。以众人望人。不敢遽以圣人责人也。如是看则其所谓众人者。固未必唤做庸众底人。亦未必唤做尧舜底人。凡有彝伦之常性分之则者。皆可以当之。其所以望人者。固未尝为拙工而废绳墨。为拙射而废彀率。明德而新民。新民而至于止至善之妙。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夫岂曰卑近而肤浅。亦岂是高远而难行也哉。古君子立言之旨。可谓上下皆通矣。御制条问曰。以己及人。圣人之仁。推己及人。学者之恕。仁与恕自有浅深大小之别。而章句引张子尽仁之语。以释忠恕之义者何也。且忠恕二字。说者不一。或谓施诸己而不愿为忠。亦勿施于人为恕。或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皆恕之事。而其实处即忠。当以何说为精也。
臣对曰仁者恕之本。恕者仁之施。仁譬则泉之源。恕譬则泉之流。故由其在我之体而及于人者。圣人之仁。推其在我之用而及于人者。学者之恕。二者之间。煞有浅深。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云者。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8L 页
 非以恕字当仁字。其曰尽仁即如孟子所谓求仁莫近焉之义耳。忠恕之释。或有就施己不愿勿施于人两句中。分属说去者。然发己自尽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合己所不愿勿施于人两句。只是一个推己及人。但所不愿已是实实底不愿。勿施是实实底勿施。这里便有个忠字在。不可以不愿句属忠。勿施句属恕。此说恐未知如何。
非以恕字当仁字。其曰尽仁即如孟子所谓求仁莫近焉之义耳。忠恕之释。或有就施己不愿勿施于人两句中。分属说去者。然发己自尽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合己所不愿勿施于人两句。只是一个推己及人。但所不愿已是实实底不愿。勿施是实实底勿施。这里便有个忠字在。不可以不愿句属忠。勿施句属恕。此说恐未知如何。御制条问曰。忠恕与中和。同欤异欤。忠为体而恕为用。忠存于内而恕行于外。则虽以忠属中。以恕属和。亦未为不可耶。且首章言道不可离而以中和结之。此章言道不远人而以忠恕结之。是必有精义之所在。可指陈欤。
臣对曰。本诸心而无伪者忠。推己心而及人者恕。则曰忠曰恕。这是心之德。天命之性无所偏倚者中。中节之情无所乖戾者和。则曰中曰和。这是性情之理。同异之别。不啻明白。岂可以体用内外之各有所当。而遽谓之忠便中而恕便和耶。首章是一篇之体要。天人性命之妙。圣神功化之极。皆本于此。所以说出道不可离而以中和字结语。此章承上文之费隐。人伦日用之常。学者求道之方。皆在于此。所以说出道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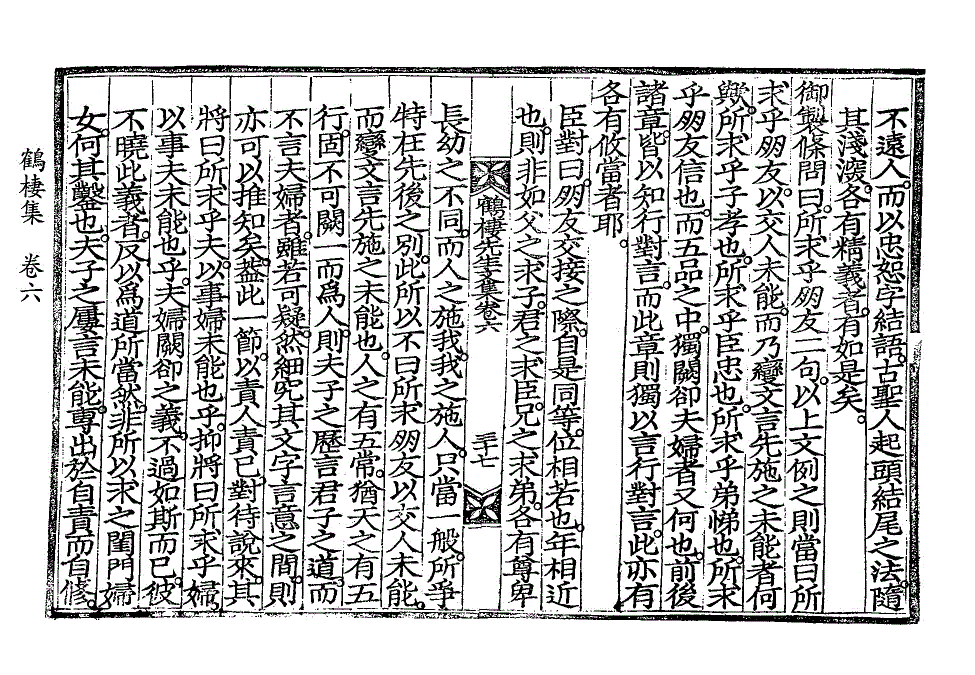 不远人。而以忠恕字结语。古圣人起头结尾之法。随其浅深。各有精义者。有如是矣。
不远人。而以忠恕字结语。古圣人起头结尾之法。随其浅深。各有精义者。有如是矣。御制条问曰。所求乎朋友二句。以上文例之则当曰所求乎朋友。以交人未能。而乃变文言先施之未能者何欤。所求乎子孝也。所求乎臣忠也。所求乎弟悌也。所求乎朋友信也。而五品之中。独阙却夫妇者又何也。前后诸章。皆以知行对言。而此章则独以言行对言。此亦有各有攸当者耶。
臣对曰。朋友交接之际。自是同等。位相若也。年相近也。则非如父之求子。君之求臣。兄之求弟。各有尊卑长幼之不同。而人之施我。我之施人。只当一般。所争特在先后之别。此所以不曰所求朋友以交人未能。而变文言先施之未能也。人之有五常。犹天之有五行。固不可阙一而为人。则夫子之历言君子之道。而不言夫妇者。虽若可疑。然细究其文字言意之间。则亦可以推知矣。盖此一节。以责人责己。对待说来。其将曰所求乎夫。以事妇未能也乎。抑将曰所求乎妇。以事夫未能也乎。夫妇阙却之义。不过如斯而已。彼不晓此义者。反以为道所当然。非所以求之闺门妇女。何其凿也。夫子之屡言未能。专出于自责而自修。
鹤栖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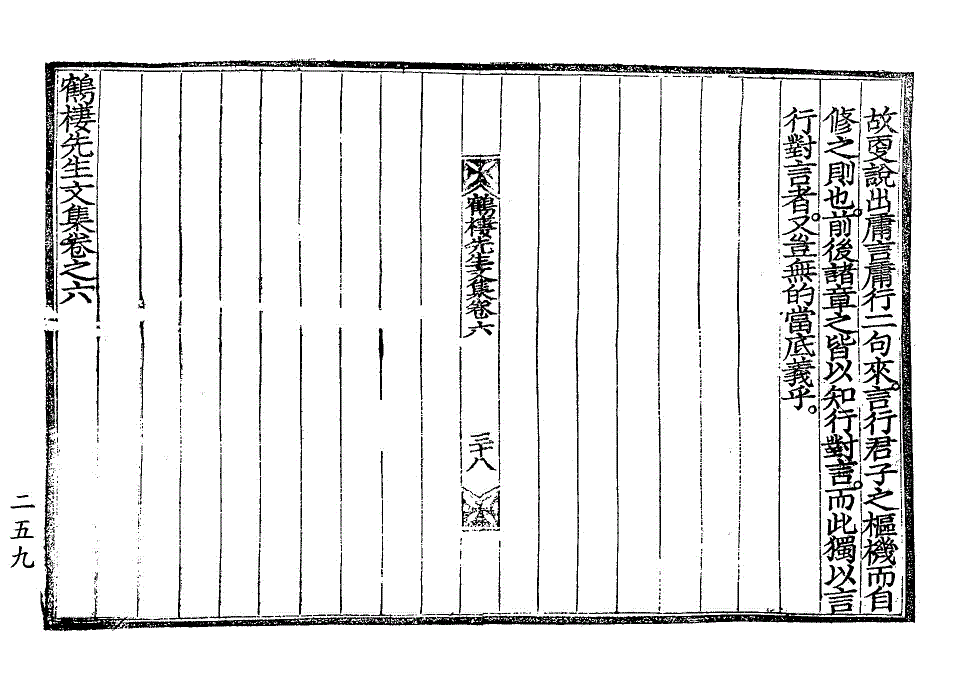 故更说出庸言庸行二句来。言行君子之枢机而自修之则也。前后诸章之皆以知行对言。而此独以言行对言者。又岂无的当底义乎。
故更说出庸言庸行二句来。言行君子之枢机而自修之则也。前后诸章之皆以知行对言。而此独以言行对言者。又岂无的当底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