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质庵集卷之四 第 x 页
质庵集卷之四(奎章阁内制)
讲义(诗传下)
讲义(诗传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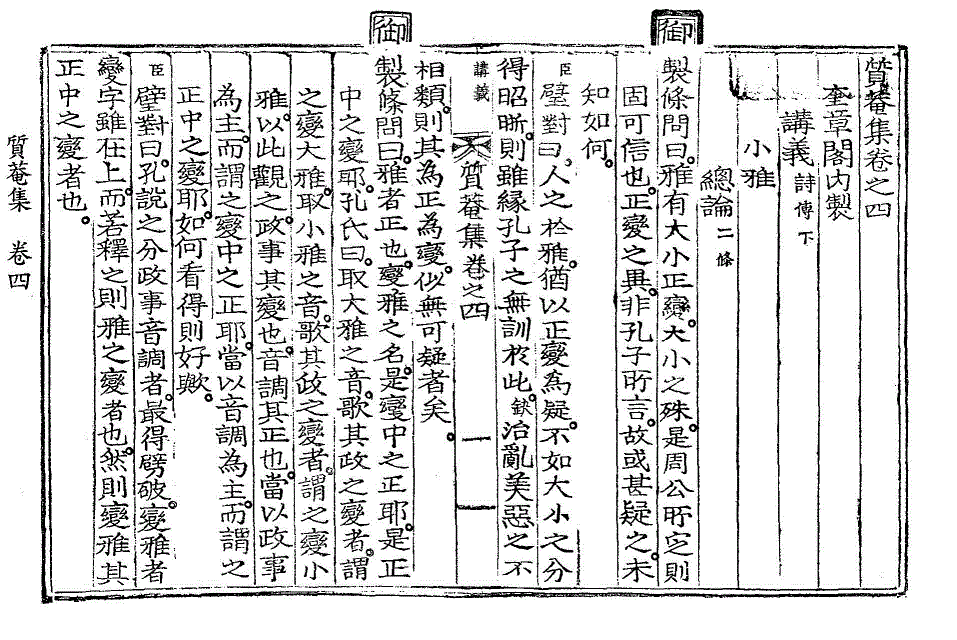 小雅
小雅总论(二条)
御制条问曰。雅有大小正变。大小之殊。是周公所定则固可信也。正变之异。非孔子所言。故或甚疑之。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人之于雅。犹以正变为疑。不如大小之分得昭晢。则虽缘孔子之无训于此。(缺)治乱美恶之不相类。则其为正为变。似无可疑者矣。
御制条问曰。雅者正也。变雅之名。是变中之正耶。是正中之变耶。孔氏曰。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谓之变小雅。以此观之。政事其变也。音调其正也。当以政事为主。而谓之变中之正耶。当以音调为主。而谓之正中之变耶。如何看得则好欤。
臣璧对曰。孔说之分政事音调者。最得劈破。变雅者变字虽在上。而若释之则雅之变者也。然则变雅其正中之变者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7L 页
 鹿鸣之什
鹿鸣之什鹿鸣(二条)
御制条问曰。大旨曰此燕飨宾客之诗也。小注庐陵李氏曰飨在庙。燕在寝。飨重而燕轻。飨则君亲献。燕则君不亲献。以此观之。燕飨是二事。鹿鸣为燕宾客而作耶。为飨宾客而作耶。朱子合而言之者何欤。虽为燕宾客而作。通用于飨礼。虽为飨宾客而作。通用于燕礼。故泛称之如此欤。
臣璧对曰。序以此为燕群臣嘉宾之诗。在群臣则可曰燕。在嘉宾则可曰飨。而于是乎鹿鸣一篇。可谓燕飨通用之乐矣。且此诗用之诸侯燕礼。用之卿大夫贡士。又用之太学之教。则何可曰为燕为飨而作也。
御制条问曰。呦呦。鹿之和声。以兴宾主之和乐。而或云是言鹿之鸣。如瑟笙之声。此说何如。首章之鼓瑟吹笙。末章之鼓瑟鼓琴。固有和乐之意。次章之德音孔昭。亦有和乐之义欤。此只以鸣字兴音字欤。
臣璧对曰。呦呦。毛传曰鹿相呼声。而集传曰声之和。其义不甚远。然则以鹿之和。兴我之致嘉宾。而以笙瑟及酒。为苹芩之兴。似好矣。不必以鹿声兴乐之声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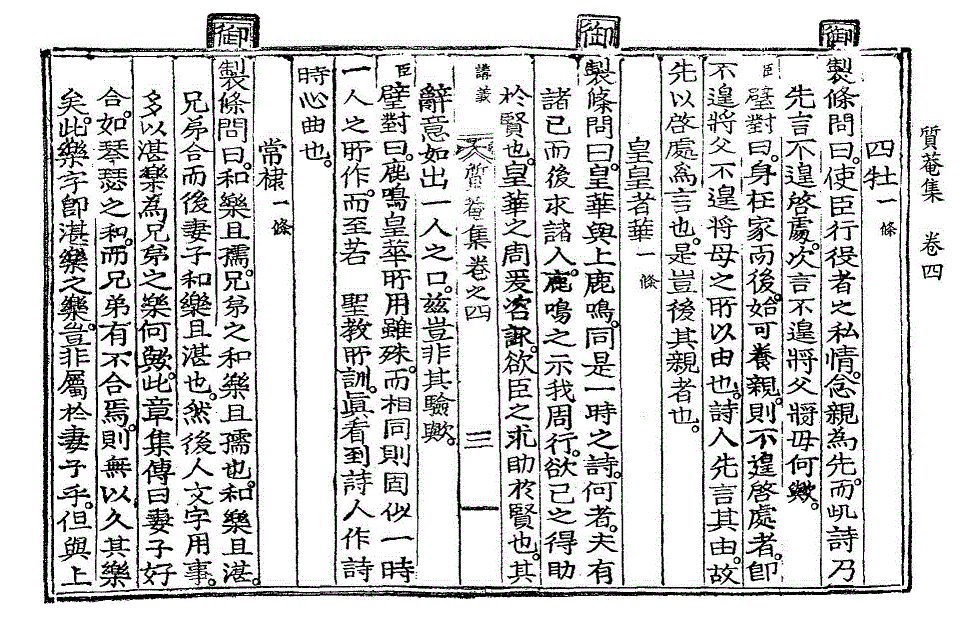 四牡(一条)
四牡(一条)御制条问曰。使臣行役者之私情。念亲为先。而此诗乃先言不遑启处。次言不遑将父将母何欤。
臣璧对曰。身在家而后。始可养亲。则不遑启处者。即不遑将父不遑将母之所以由也。诗人先言其由。故先以启处为言也。是岂后其亲者也。
皇皇者华(一条)
御制条问曰。皇华与上鹿鸣。同是一时之诗。何者。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鹿鸣之示我周行。欲己之得助于贤也。皇华之周爰咨诹。欲臣之求助于贤也。其辞意如出一人之口。玆岂非其验欤。
臣璧对曰。鹿鸣皇华所用虽殊。而相同则固似一时一人之所作。而至若 圣教所训。真看到诗人作诗时心曲也。
常棣(一条)
御制条问曰。和乐且孺。兄弟之和乐且孺也。和乐且湛。兄弟合而后妻子和乐且湛也。然后人文字用事。多以湛乐为兄弟之乐何欤。此章集传曰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则无以久其乐矣。此乐字即湛乐之乐。岂非属于妻子乎。但与上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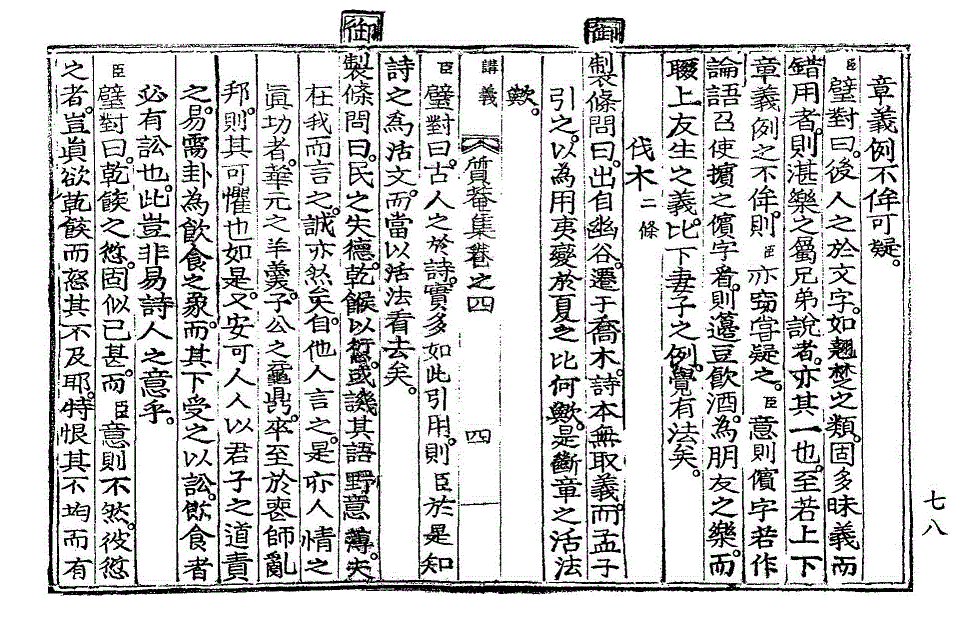 章义例不侔可疑。
章义例不侔可疑。臣璧对曰。后人之于文字。如翘楚之类。固多昧义而错用者。则湛乐之属兄弟说者。亦其一也。至若上下章义例之不侔。则臣亦窃尝疑之。臣意则傧字若作论语召使摈之傧字看。则笾豆饮酒。为朋友之乐。而联上友生之义。比下妻子之例。觉有法矣。
伐木(二条)
御制条问曰。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诗本无取义。而孟子引之。以为用夷变于夏之比何欤。是断章之活法欤。
臣璧对曰。古人之于诗。实多如此引用。则臣于是知诗之为活文。而当以活法看去矣。
御制条问曰。民之失德。乾糇以愆。或讥其语野意薄。夫在我而言之。诚亦然矣。自他人言之。是亦人情之真切者。华元之羊羹。子公之鼋鼎。卒至于丧师乱邦。则其可惧也如是。又安可人人以君子之道责之。易需卦为饮食之象。而其下受之以讼。饮食者必有讼也。此岂非易诗人之意乎。
臣璧对曰。乾糇之愆。固似已甚。而臣意则不然。彼愆之者。岂真欲乾糇而怒其不及耶。特恨其不均而有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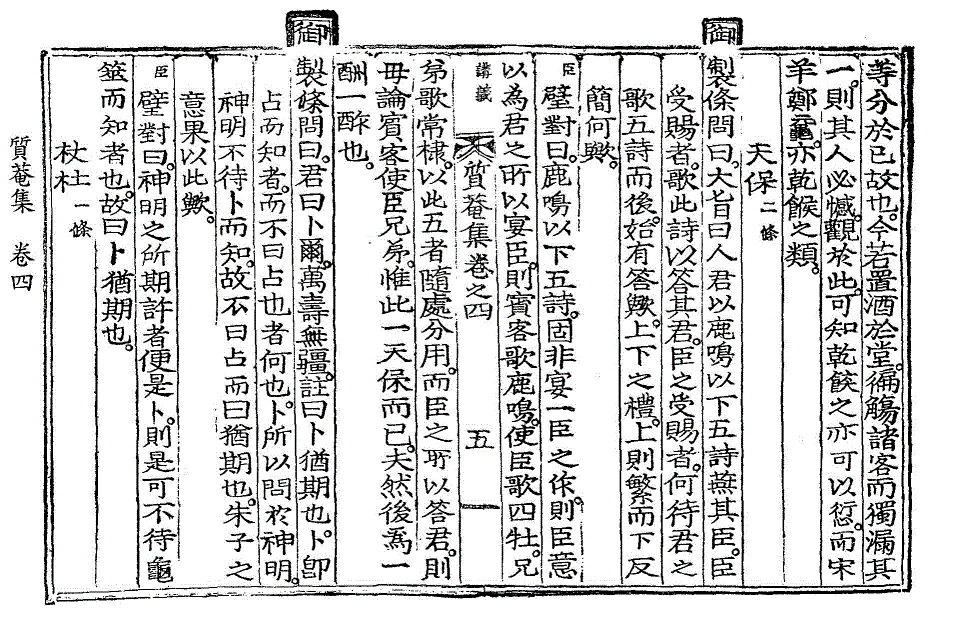 等分于己故也。今若置酒于堂。遍觞诸客而独漏其一。则其人必憾。观于此。可知乾糇之亦可以愆。而宋羊郑鼋。亦乾糇之类。
等分于己故也。今若置酒于堂。遍觞诸客而独漏其一。则其人必憾。观于此。可知乾糇之亦可以愆。而宋羊郑鼋。亦乾糇之类。天保(二条)
御制条问曰。大旨曰人君以鹿鸣以下五诗燕其臣。臣受赐者。歌此诗以答其君。臣之受赐者。何待君之歌五诗而后。始有答欤。上下之礼。上则繁而下反简何欤。
臣璧对曰。鹿鸣以下五诗。固非宴一臣之作。则臣意以为君之所以宴臣。则宾客歌鹿鸣。使臣歌四牡。兄弟歌常棣。以此五者随处分用。而臣之所以答君。则毋论宾客使臣兄弟。惟此一天保而已。夫然后为一酬一酢也。
御制条问曰。君曰卜尔。万寿无疆。注曰卜犹期也。卜即占而知者。而不曰占也者何也。卜所以问于神明。神明不待卜而知。故不曰占而曰犹期也。朱子之意果以此欤。
臣璧对曰。神明之所期许者便是卜。则是可不待龟筮而知者也。故曰卜犹期也。
杖杜(一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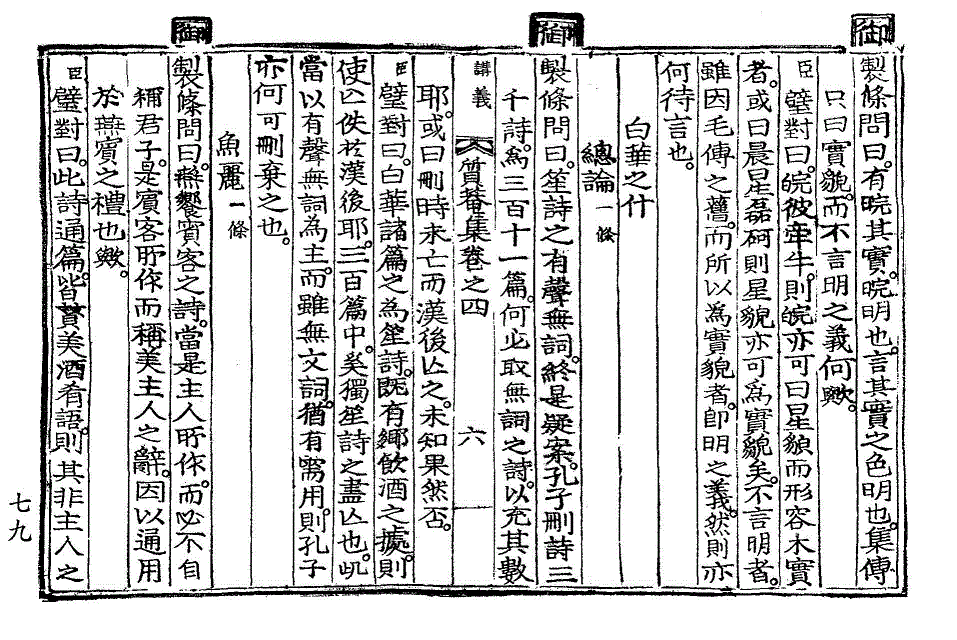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有皖其实。皖明也。言其实之色明也。集传只曰实貌。而不言明之义何欤。
御制条问曰。有皖其实。皖明也。言其实之色明也。集传只曰实貌。而不言明之义何欤。臣璧对曰。皖彼牵牛。则皖亦可曰星貌而形容木实者。或曰晨星磊砢则星貌亦可为实貌矣。不言明者。虽因毛传之旧。而所以为实貌者。即明之义。然则亦何待言也。
白华之什
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笙诗之有声无词。终是疑案。孔子删诗三千诗。为三百十一篇。何必取无词之诗。以充其数耶。或曰删时未亡而汉后亡之。未知果然否。
臣璧对曰。白华诸篇之为笙诗。既有乡饮酒之据。则使亡佚于汉后耶。三百篇中。奚独笙诗之尽亡也。此当以有声无词为主。而虽无文词。犹有需用。则孔子亦何可删弃之也。
鱼丽(一条)
御制条问曰。燕飨宾客之诗。当是主人所作。而必不自称君子。是宾客所作而称美主人之辞。因以通用于燕宾之礼也欤。
臣璧对曰。此诗通篇。皆赞美酒肴语。则其非主人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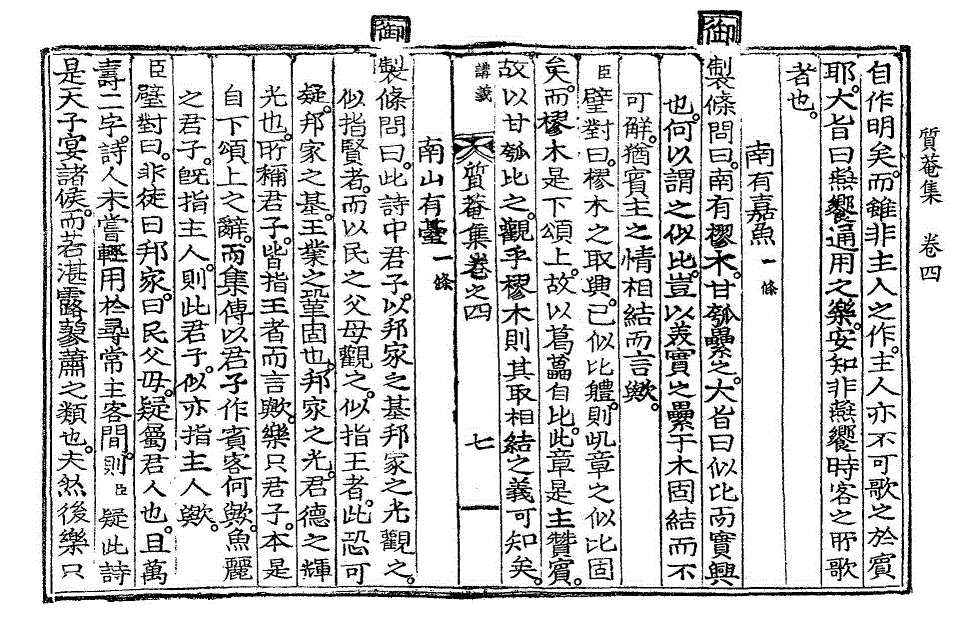 自作明矣。而虽非主人之作。主人亦不可歌之于宾耶。大旨曰燕飨通用之乐。安知非燕飨时客之所歌者也。
自作明矣。而虽非主人之作。主人亦不可歌之于宾耶。大旨曰燕飨通用之乐。安知非燕飨时客之所歌者也。南有嘉鱼(一条)
御制条问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大旨曰似比而实兴也。何以谓之似比。岂以美实之累于木固结而不可解。犹宾主之情相结而言欤。
臣璧对曰。樛木之取兴。已似比体。则此章之似比固矣。而樛木是下颂上。故以葛藟自比。此章是主赞宾。故以甘瓠比之。观乎樛木则其取相结之义可知矣。
南山有台(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中君子。以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观之。似指贤者。而以民之父母观之。似指王者。此恐可疑。邦家之基。王业之巩固也。邦家之光。君德之辉光也。所称君子。皆指王者而言欤。乐只君子。本是自下颂上之辞。而集传以君子作宾客何欤。鱼丽之君子。既指主人。则此君子。似亦指主人欤。
臣璧对曰。非徒曰邦家。曰民父母。疑属君人也。且万寿二字。诗人未尝轻用于寻常主客间。则臣疑此诗是天子宴诸侯。而若湛露蓼萧之类也。夫然后乐只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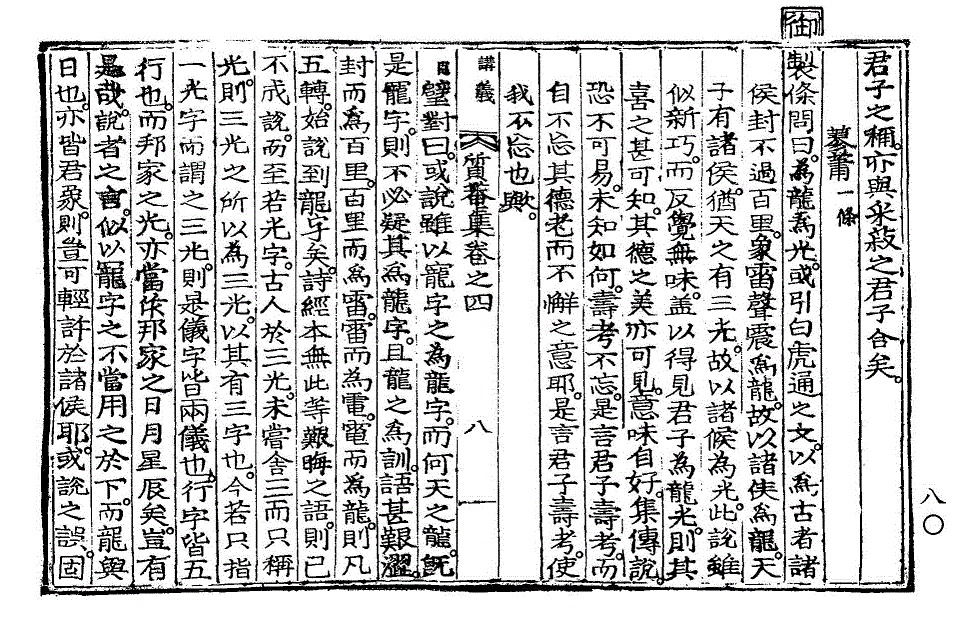 君子之称。亦与采菽之君子合矣。
君子之称。亦与采菽之君子合矣。蓼萧(一条)
御制条问曰。为龙为光。或引白虎通之文。以为古者诸侯封不过百里。象雷声震为龙。故以诸侯为龙。天子有诸侯。犹天之有三光。故以诸侯为光。此说虽似新巧。而反觉无味。盖以得见君子为龙光。则其喜之甚可知。其德之美亦可见。意味自好。集传说。恐不可易。未知如何。寿考不忘。是言君子寿考。而自不忘其德老而不懈之意耶。是言君子寿考。使我不忘也欤。
臣璧对曰。或说虽以宠字之为龙字。而何天之龙。既是宠字。则不必疑其为龙字。且龙之为训。语甚艰涩。封而为百里。百里而为雷。雷而为电。电而为龙。则凡五转。始说到龙字矣。诗经本无此等艰晦之语。则已不成说。而至若光字。古人于三光。未尝舍三而只称光。则三光之所以为三光。以其有三字也。今若只指一光字而谓之三光。则是仪字皆两仪也。行字皆五行也。而邦家之光。亦当作邦家之日月星辰矣。岂有是哉。说者之言。似以宠字之不当用之于下。而龙与日也。亦皆君象。则岂可轻许于诸侯耶。或说之误。固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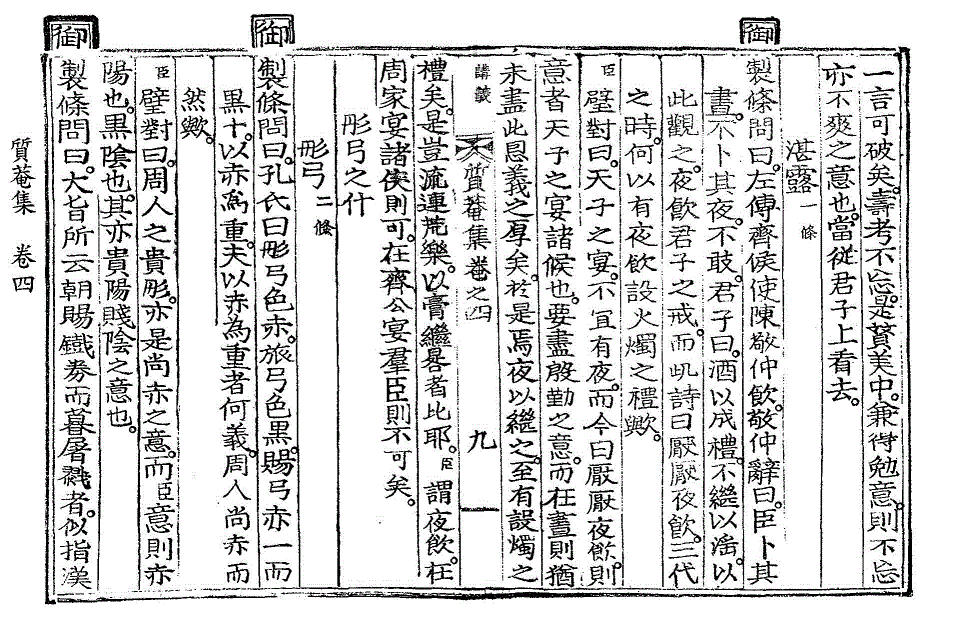 一言可破矣。寿考不忘。是赞美中。兼得勉意。则不忘亦不爽之意也。当从君子上看去。
一言可破矣。寿考不忘。是赞美中。兼得勉意。则不忘亦不爽之意也。当从君子上看去。湛露(一条)
御制条问曰。左传齐侯使陈敬仲饮。敬仲辞曰。臣卜其昼。不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以此观之。夜饮君子之戒。而此诗曰厌厌夜饮。三代之时。何以有夜饮设火烛之礼欤。
臣璧对曰。天子之宴。不宜有夜。而今曰厌厌夜饮。则意者天子之宴诸侯也。要尽殷勤之意。而在昼则犹未尽此恩义之厚矣。于是焉夜以继之。至有设烛之礼矣。是岂流连荒乐。以膏继晷者比耶。臣谓夜饮。在周家宴诸侯则可。在齐公宴群臣则不可矣。
彤弓之什
彤弓(二条)
御制条问曰。孔氏曰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赐弓赤一而黑十。以赤为重。夫以赤为重者何义。周人尚赤而然欤。
臣璧对曰。周人之贵彤。亦是尚赤之意。而臣意则赤阳也。黑阴也。其亦贵阳贱阴之意也。
御制条问曰。大旨所云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似指汉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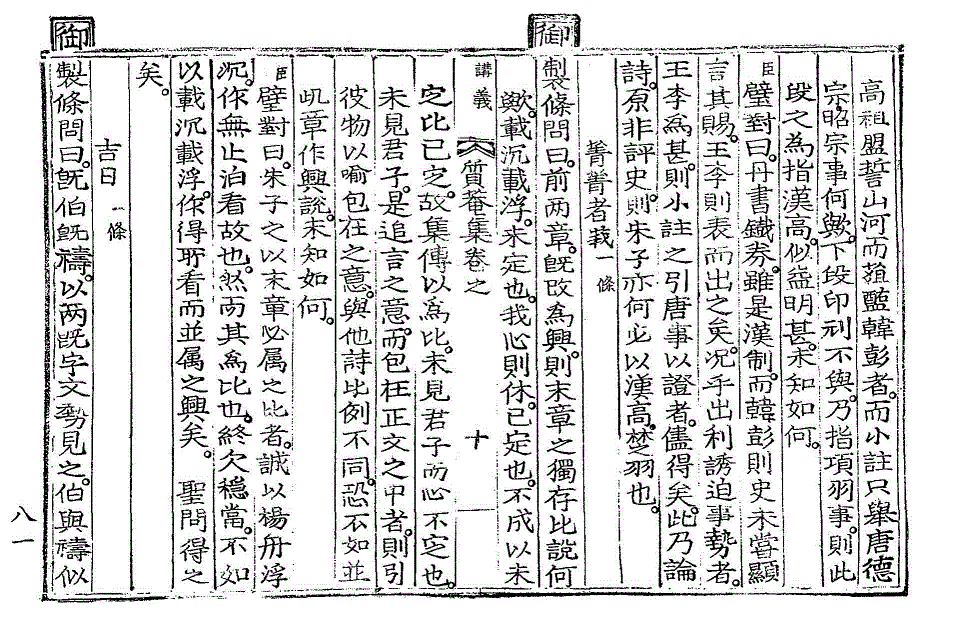 高祖盟誓山河而菹醢韩彭者。而小注只举唐德宗,昭宗事何欤。下段印刓不与。乃指项羽事。则此段之为指汉高。似益明甚。未知如何。
高祖盟誓山河而菹醢韩彭者。而小注只举唐德宗,昭宗事何欤。下段印刓不与。乃指项羽事。则此段之为指汉高。似益明甚。未知如何。臣璧对曰。丹书铁券。虽是汉制。而韩彭则史未尝显言其赐。王李则表而出之矣。况乎出利诱迫事势者。王李为甚。则小注之引唐事以證者。尽得矣。此乃论诗。原非评史。则朱子亦何必以汉高,楚羽也。
菁菁者莪(一条)
御制条问曰。前两章。既改为兴。则末章之独存比说何欤。载沉载浮。未定也。我心则休。已定也。不成以未定比已定。故集传以为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未见君子。是追言之意。而包在正文之中者。则引彼物以喻包在之意。与他诗比例不同。恐不如并此章作兴说。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朱子之以末章必属之比者。诚以杨舟浮沉。作无止泊看故也。然而其为比也。终欠稳当。不如以载沉载浮。作得所看而并属之兴矣。 圣问得之矣。
吉日(一条)
御制条问曰。既伯既祷。以两既字文势见之。伯与祷似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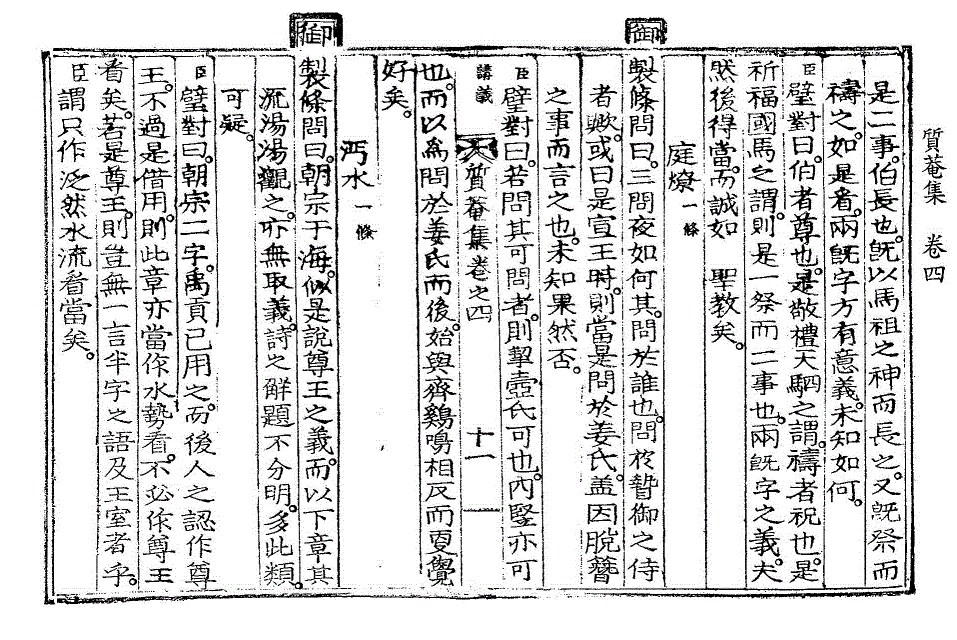 是二事。伯长也。既以马祖之神而长之。又既祭而祷之。如是看。两既字方有意义。未知如何。
是二事。伯长也。既以马祖之神而长之。又既祭而祷之。如是看。两既字方有意义。未知如何。臣璧对曰。伯者尊也。是敬礼天驷之谓。祷者祝也。是祈福国马之谓。则是一祭而二事也。两既字之义。夫然后得当。而诚如 圣教矣。
庭燎(一条)
御制条问曰。三问夜如何其。问于谁也。问于亵御之侍者欤。或曰是宣王时。则当是问于姜氏。盖因脱簪之事而言之也。未知果然否。
臣璧对曰。若问其可问者。则挈壶氏可也。内竖亦可也。而以为问于姜氏而后。始与齐鸡鸣相反而更觉好矣。
沔水(一条)
御制条问曰。朝宗于海。似是说尊王之义。而以下章其流汤汤观之。亦无取义。诗之解题不分明。多此类。可疑。
臣璧对曰。朝宗二字。禹贡已用之。而后人之认作尊王。不过是借用。则此章亦当作水势看。不必作尊王看矣。若是尊王。则岂无一言半字之语及王室者乎。臣谓只作泛然水流看当矣。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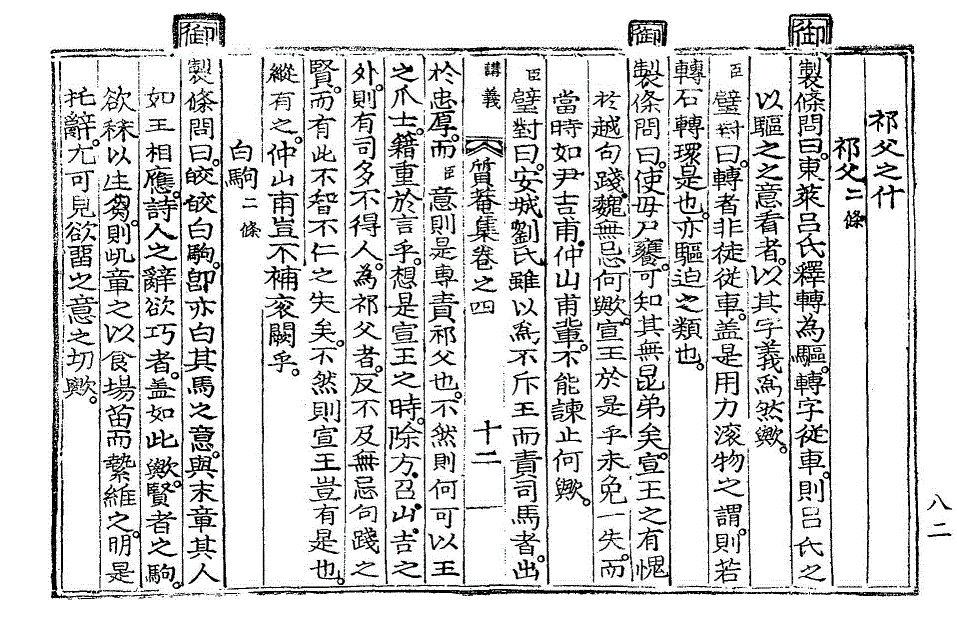 祁父之什
祁父之什祁父(二条)
御制条问曰。东莱吕氏释转为驱。转字从车。则吕氏之以驱之之意看者。以其字义为然欤。
臣璧对曰。转者非徒从车。盖是用力滚物之谓。则若转石转环是也。亦驱迫之类也。
御制条问曰。使母尸饔。可知其无昆弟矣。宣王之有愧于越句践,魏无忌何欤。宣王于是乎未免一失。而当时如尹吉甫,仲山甫辈。不能谏止何欤。
臣璧对曰。安城刘氏虽以为不斥王而责司马者。出于忠厚。而臣意则是专责祁父也。不然则何可以王之爪士。籍重于言乎。想是宣王之时。除方,召,山,吉之外。则有司多不得人。为祁父者。反不及无忌句践之贤。而有此不智不仁之失矣。不然则宣王岂有是也。纵有之。仲山甫岂不补衮阙乎。
白驹(二条)
御制条问曰。皎皎白驹。即亦白其马之意。与末章其人如王相应。诗人之辞欲巧者。盖如此欤。贤者之驹。欲秣以生刍。则此章之以食场苗而絷维之。明是托辞。尤可见欲留之意之切欤。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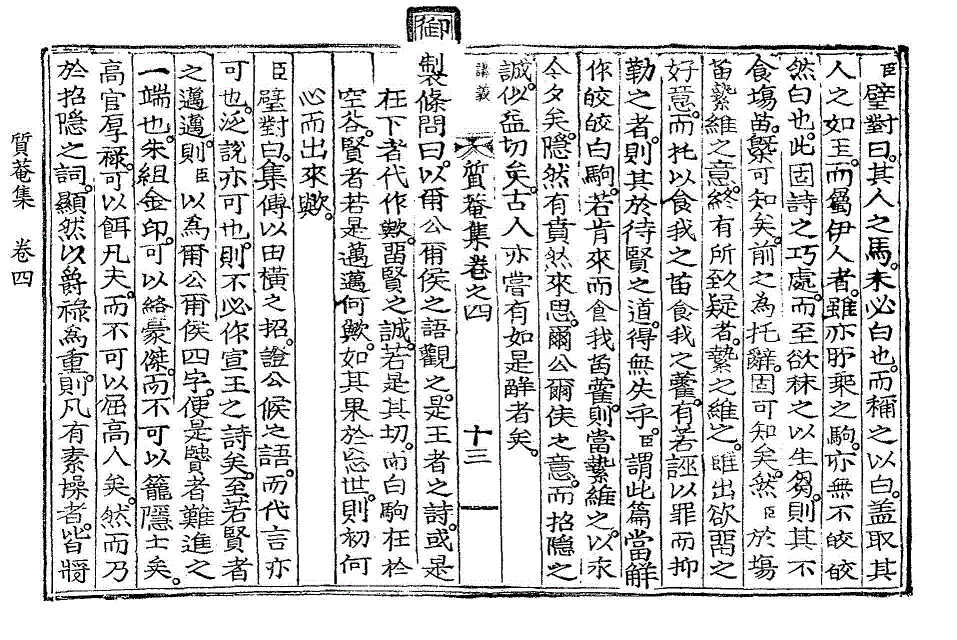 臣璧对曰。其人之马。未必白也。而称之以白。盖取其人之如玉。而属伊人者。虽亦所乘之驹。亦无不皎皎然白也。此固诗之巧处。而至欲秣之以生刍。则其不食场苗。槩可知矣。前之为托辞。固可知矣。然臣于场苗絷维之意。终有所致疑者。絷之维之。虽出欲留之好意。而托以食我之苗食我之藿。有若诬以罪而抑勒之者。则其于待贤之道。得无失乎。臣谓此篇当解作皎皎白驹。若肯来而食我苗藿。则当絷维之。以永今夕矣。隐然有贲然来思。尔公尔侯之意。而招隐之诚。似益切矣。古人亦尝有如是解者矣。
臣璧对曰。其人之马。未必白也。而称之以白。盖取其人之如玉。而属伊人者。虽亦所乘之驹。亦无不皎皎然白也。此固诗之巧处。而至欲秣之以生刍。则其不食场苗。槩可知矣。前之为托辞。固可知矣。然臣于场苗絷维之意。终有所致疑者。絷之维之。虽出欲留之好意。而托以食我之苗食我之藿。有若诬以罪而抑勒之者。则其于待贤之道。得无失乎。臣谓此篇当解作皎皎白驹。若肯来而食我苗藿。则当絷维之。以永今夕矣。隐然有贲然来思。尔公尔侯之意。而招隐之诚。似益切矣。古人亦尝有如是解者矣。御制条问曰。以尔公尔侯之语观之。是王者之诗。或是在下者代作欤。留贤之诚。若是其切。而白驹在于空谷。贤者若是迈迈何欤。如其果于忘世。则初何心而出来欤。
臣璧对曰。集传以田横之招。證公侯之语。而代言亦可也。泛说亦可也。则不必作宣王之诗矣。至若贤者之迈迈。则臣以为尔公尔侯四字。便是贤者难进之一端也。朱组金印。可以络豪杰。而不可以笼隐士矣。高官厚禄。可以饵凡夫。而不可以屈高人矣。然而乃于招隐之词。显然以爵禄为重。则凡有素操者。皆将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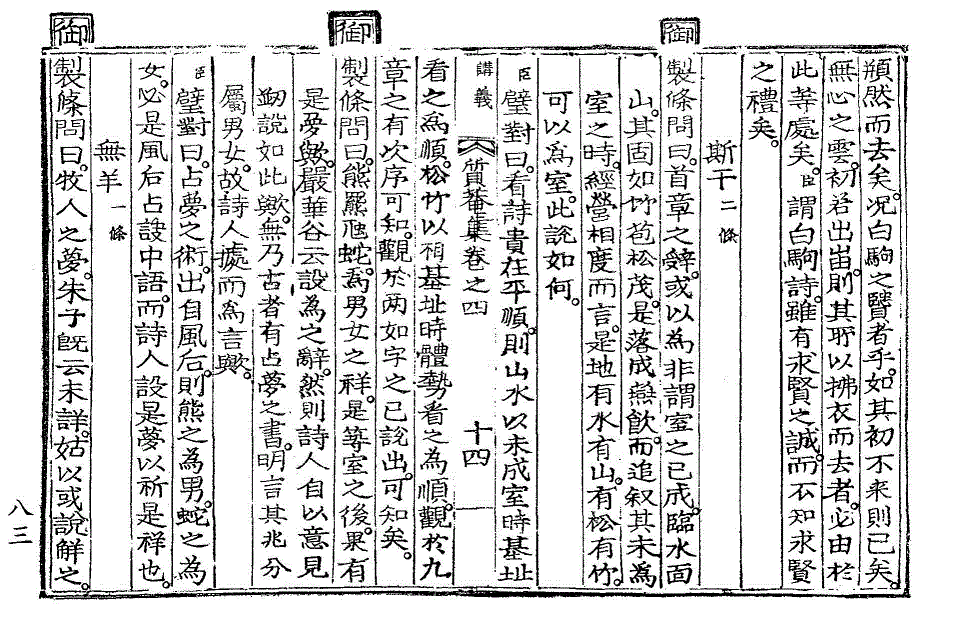 頩然而去矣。况白驹之贤者乎。如其初不来则已矣。无心之云。初若出岫。则其所以拂衣而去者。必由于此等处矣。臣谓白驹诗。虽有求贤之诚。而不知求贤之礼矣。
頩然而去矣。况白驹之贤者乎。如其初不来则已矣。无心之云。初若出岫。则其所以拂衣而去者。必由于此等处矣。臣谓白驹诗。虽有求贤之诚。而不知求贤之礼矣。斯干(二条)
御制条问曰。首章之辞。或以为非谓室之已成。临水面山。其固如竹苞松茂。是落成燕饮。而追叙其未为室之时。经营相度而言。是地有水有山。有松有竹。可以为室。此说如何。
臣璧对曰。看诗贵在平顺。则山水以未成室时基址看之为顺。松竹以相基址时体势看之为顺。观于九章之有次序可知。观于两如字之已说出。可知矣。
御制条问曰。熊罴虺蛇。为男女之祥。是筑室之后。果有是梦欤。严华谷云设为之辞。然则诗人自以意见刱说如此欤。无乃古者有占梦之书。明言其兆分属男女。故诗人据而为言欤。
臣璧对曰。占梦之术。出自风后。则熊之为男。蛇之为女。必是风后占诀中语。而诗人设是梦以祈是祥也。
无羊(一条)
御制条问曰。牧人之梦。朱子既云未详。姑以或说解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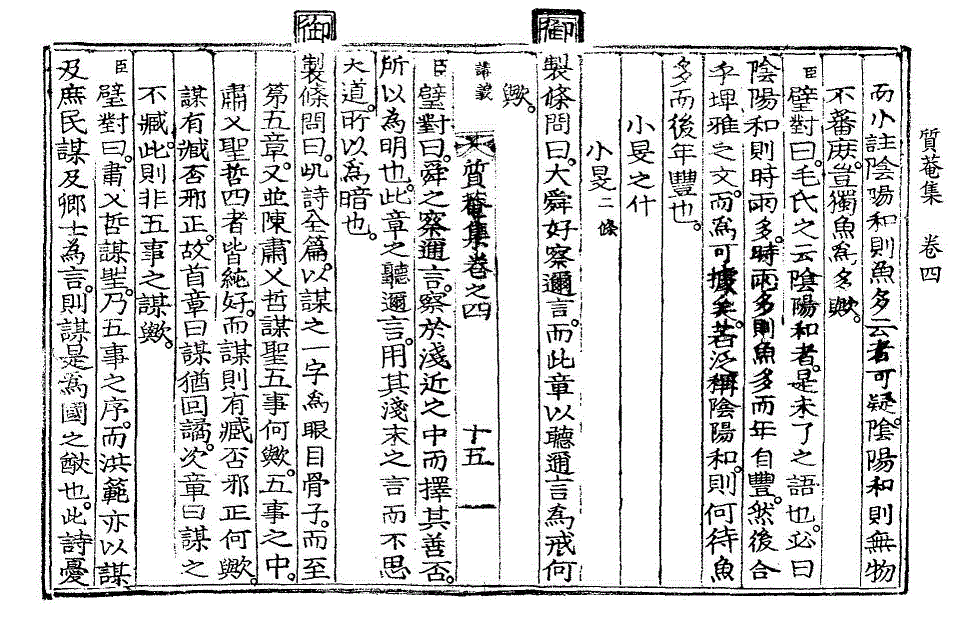 而小注阴阳和则鱼多云者可疑。阴阳和则无物不蕃庶。岂独鱼为多欤。
而小注阴阳和则鱼多云者可疑。阴阳和则无物不蕃庶。岂独鱼为多欤。臣璧对曰。毛氏之云阴阳和者。是未了之语也。必曰阴阳和则时雨多。时雨多则鱼多而年自丰。然后合乎埤雅之文。而为可据矣。若泛称阴阳和。则何待鱼多而后年丰也。
小旻之什
小旻(二条)
御制条问曰。大舜好察迩言。而此章以听迩言为戒何欤。
臣璧对曰。舜之察迩言。察于浅近之中而择其善否。所以为明也。此章之听迩言。用其浅末之言而不思大道。所以为暗也。
御制条问曰。此诗全篇。以谋之一字为眼目骨子。而至第五章。又并陈肃乂哲谋圣五事何欤。五事之中。肃乂圣哲四者皆纯好。而谋则有臧否邪正何欤。谋有臧否邪正。故首章曰谋犹回谲。次章曰谋之不臧。此则非五事之谋欤。
臣璧对曰。肃乂哲谋圣。乃五事之序。而洪范亦以谋及庶民谋及卿士为言。则谋是为国之猷也。此诗忧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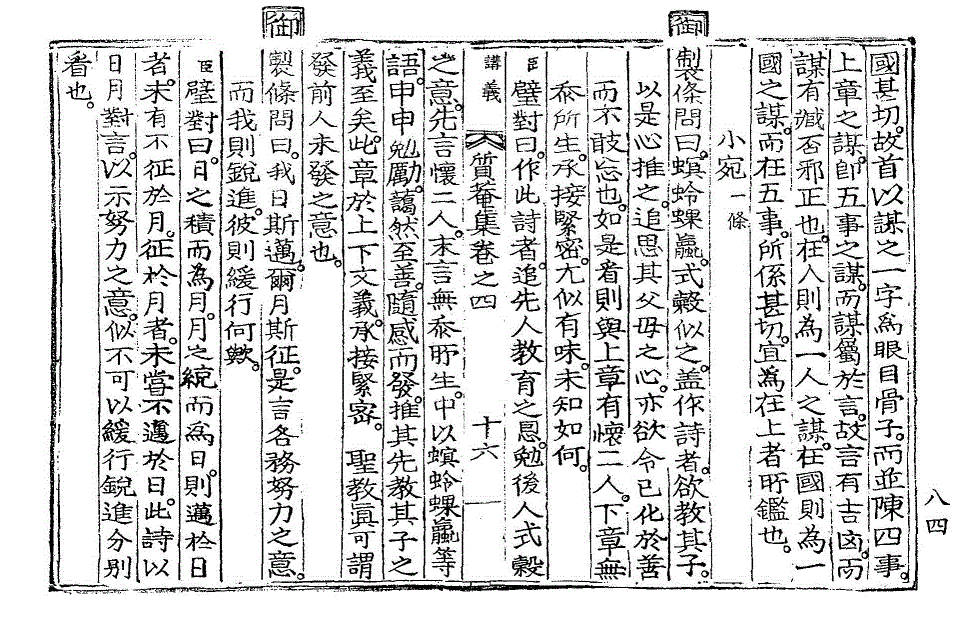 国甚切。故首以谋之一字为眼目骨子。而并陈四事。上章之谋。即五事之谋。而谋属于言。故言有吉凶。而谋有臧否邪正也。在人则为一人之谋。在国则为一国之谋。而在五事。所系甚切。宜为在上者所鉴也。
国甚切。故首以谋之一字为眼目骨子。而并陈四事。上章之谋。即五事之谋。而谋属于言。故言有吉凶。而谋有臧否邪正也。在人则为一人之谋。在国则为一国之谋。而在五事。所系甚切。宜为在上者所鉴也。小宛 一(一作二)条
御制条问曰。螟蛉蜾蠃。式谷似之。盖作诗者。欲教其子。以是心推之。追思其父母之心。亦欲令己化于善而不敢忘也。如是看则与上章有怀二人。下章无忝所生。承接紧密。尤似有味。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作此诗者。追先人教育之恩。勉后人式谷之意。先言怀二人。末言无忝所生。中以螟蛉蜾蠃等语。申申勉励。蔼然至善。随感而发。推其先教其子之义至矣。此章于上下文义。承接紧密。 圣教真可谓发前人未发之意也。
御制条问曰。我日斯迈。尔月斯征。是言各务努力之意。而我则锐进。彼则缓行何欤。
臣璧对曰。日之积而为月。月之统而为日。则迈于日者。未有不征于月。征于月者。未尝不迈于日。此诗以日月对言。以示努力之意。似不可以缓行锐进分别看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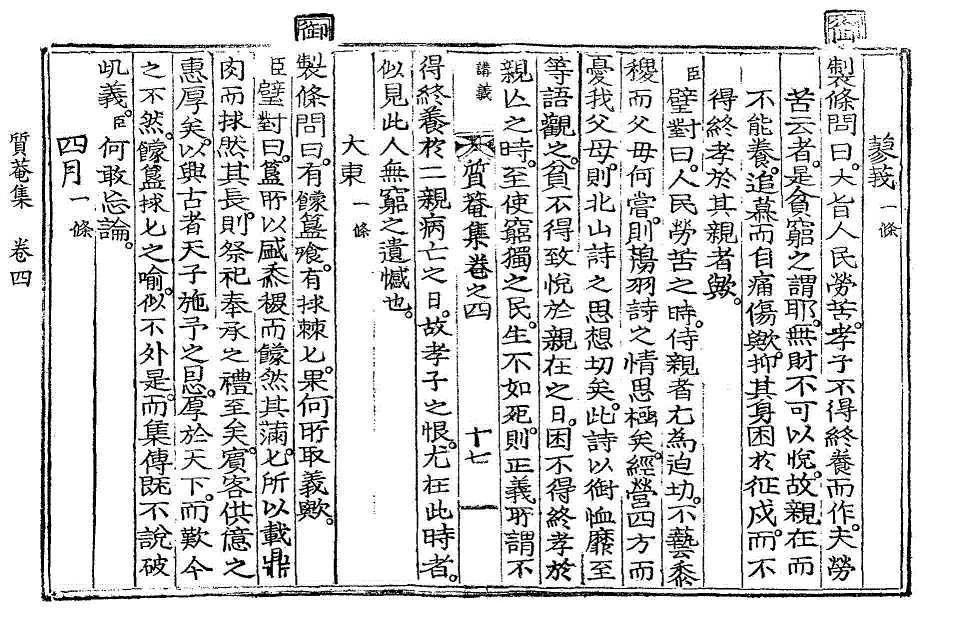 蓼莪(一条)
蓼莪(一条)御制条问曰。大旨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夫劳苦云者。是贫穷之谓耶。无财不可以悦。故亲在而不能养。追慕而自痛伤欤。抑其身困于征戍。而不得终孝于其亲者欤。
臣璧对曰。人民劳苦之时。侍亲者尤为迫切。不艺黍稷而父母何尝。则鸨羽诗之情思极矣。经营四方而忧我父母。则北山诗之思想切矣。此诗以衔恤靡至等语观之。贫不得致悦于亲在之日。困不得终孝于亲亡之时。至使穷独之民。生不如死。则正义所谓不得终养于二亲病亡之日。故孝子之恨。尤在此时者。似见此人无穷之遗憾也。
大东(一条)
御制条问曰。有饛簋飧。有救棘匕。果何所取义欤。
臣璧对曰。簋所以盛黍稷而饛然其满。匕所以载鼎肉而救然其长。则祭祀奉承之礼至矣。宾客供亿之惠厚矣。以兴古者天子施予之恩。厚于天下。而叹今之不然。饛簋救匕之喻。似不外是。而集传既不说破此义。臣何敢忘论。
四月(一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5L 页
 御制条问曰。以山有嘉卉为兴。则是言国有残贼之臣。 异乎山之有嘉卉也欤。
御制条问曰。以山有嘉卉为兴。则是言国有残贼之臣。 异乎山之有嘉卉也欤。臣璧对曰。山之卉国之贼。旧说虽作閒漫说。而要之不过以国有残贼。叹不如山之有嘉卉也。
北山之什
北山(一条)
御制条问曰。独贤独劳也。上章曰偕偕士子。下章曰膂力方刚。既是强壮之人。则足任事务之繁。何惮于劳苦而必怨之欤。且夫君子之心。不愿佚乐。而诗人之言如此者何欤。
臣璧对曰。劳于王事者。臣子之职。而况膂力刚壮。足任事务。则诗人岂敢有惮殃之怨哉。然而劳逸不均。未见共供之事。使役无常。不闻同寅之义。使君子任其忧。小人享其乐。则独贤之怨。安得不发于从事劳苦之时乎。诗可以怨。政为此类。而宜为在上者之所鉴也。
楚茨(一条)
御制条问曰。永锡尔极之极。恐非众善之极。而极犹言福也。时万时亿之万。恐非万事之谓。而万是言寿也。盖曰永锡尔诸福之极。俾享万亿之寿也。如是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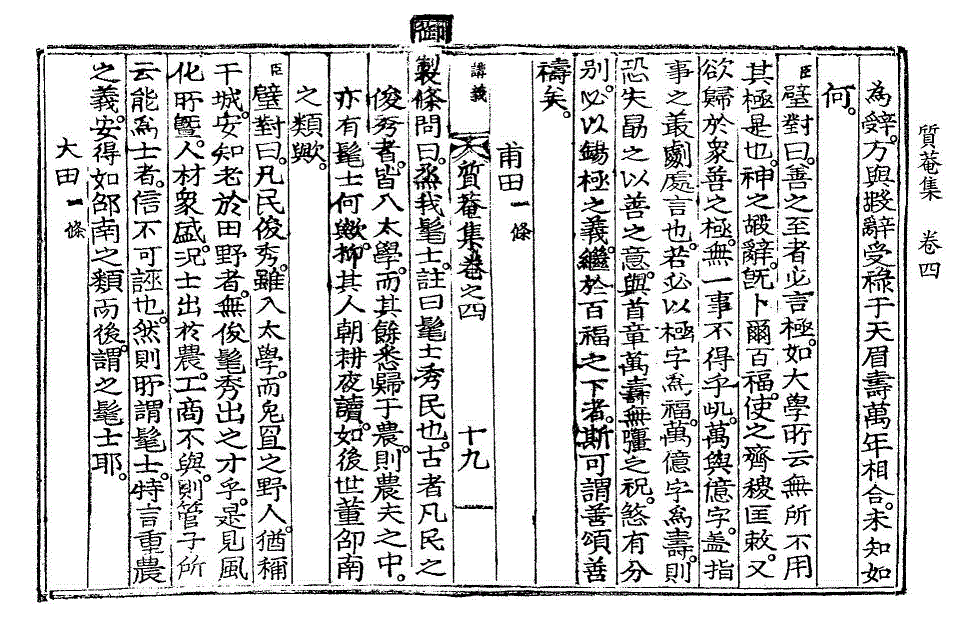 为辞。方与嘏辞受禄于天眉寿万年相合。未知如何。
为辞。方与嘏辞受禄于天眉寿万年相合。未知如何。臣璧对曰。善之至者必言极。如大学所云无所不用其极是也。神之嘏辞。既卜尔百福。使之齐稷匡敕。又欲归于众善之极。无一事不得乎此。万与亿字。盖指事之丛剧处言也。若必以极字为福。万亿字为寿。则恐失勖之以善之意。与首章万寿无彊之祝。煞有分别。必以锡极之义。继于百福之下者。斯可谓善颂善祷矣。
甫田(一条)
御制条问曰。烝我髦士。注曰髦士秀民也。古者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太学。而其馀悉归于农。则农夫之中。亦有髦士何欤。抑其人朝耕夜读。如后世董邵南之类欤。
臣璧对曰。凡民俊秀。虽入太学。而兔罝之野人。犹称干城。安知老于田野者。无俊髦秀出之才乎。是见风化所暨。人材众盛。况士出于农。工商不与。则管子所云能为士者。信不可诬也。然则所谓髦士。特言重农之义。安得如邵南之类而后。谓之髦士耶。
大田(一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6L 页
 御制条问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何其与七月篇献豜于公。言私其豵之语意相类。以此观之。明是为豳雅。而朱子盖尝以为断无他疑。又于此篇之后。题曰亦未知其是否。议论之如是未定何欤。
御制条问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何其与七月篇献豜于公。言私其豵之语意相类。以此观之。明是为豳雅。而朱子盖尝以为断无他疑。又于此篇之后。题曰亦未知其是否。议论之如是未定何欤。臣璧对曰。周家以田功开国。而豳风为农功首事。故雅颂之中。凡为农事作。皆可冠以豳号。此诗备言稼穑之功。又明公私之分。与豳风八章。体裁不异。所以疑其豳雅。而诗中公田曾孙等语。与豳人草创时辞气。煞有分别。恐不可直以豳雅断之也。集传议论之未定。其以是耶。
瞻彼洛矣(一条)
御制条问曰。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而此诗只以讲武事。为万年保邦之道何欤。有文章者。必有武备。武事是讲。则其必先有文章可知故欤。
臣璧对曰。有文事而不忘武备。乃为享福禄保国家之道。周家文章。如是彬蔚。而岂有专尚武事耶。讲武事而先有文章。诚如 圣教矣。
桑扈之什
桑扈(一条)
御制条问曰。有莺其羽。注曰莺然有文章。是以桑扈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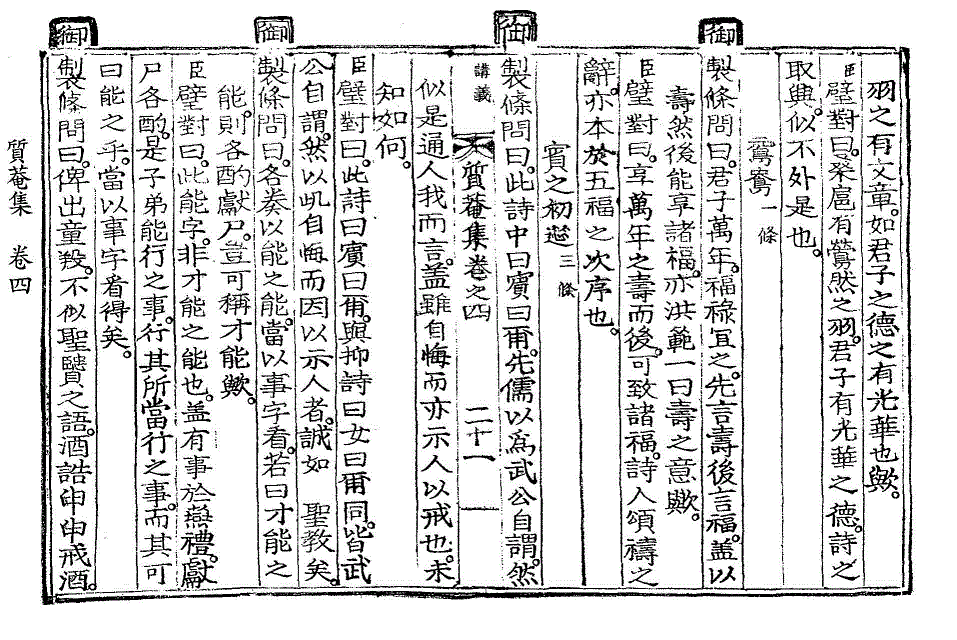 羽之有文章。如君子之德之有光华也欤。
羽之有文章。如君子之德之有光华也欤。臣璧对曰。桑扈有莺然之羽。君子有光华之德。诗之取兴。似不外是也。
䲶鸯(一条)
御制条问曰。君子万年。福禄宜之。先言寿后言福。盖以寿然后能享诸福。亦洪范一曰寿之意欤。
臣璧对曰。享万年之寿而后。可致诸福。诗人颂祷之辞。亦本于五福之次序也。
宾之初筵(三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中曰宾曰尔。先儒以为武公自谓。然似是通人我而言。盖虽自悔而亦示人以戒也。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诗曰宾曰尔。与抑诗曰女曰尔同。皆武公自谓。然以此自悔而因以示人者。诚如 圣教矣。
御制条问曰。各奏以能之能。当以事字看。若曰才能之能。则各酌献尸。岂可称才能欤。
臣璧对曰。此能字。非才能之能也。盖有事于燕礼。献尸各酌。是子弟能行之事。行其所当行之事。而其可曰能之乎。当以事字看得矣。
御制条问曰。俾出童羖。不似圣贤之语。酒诰申申戒酒。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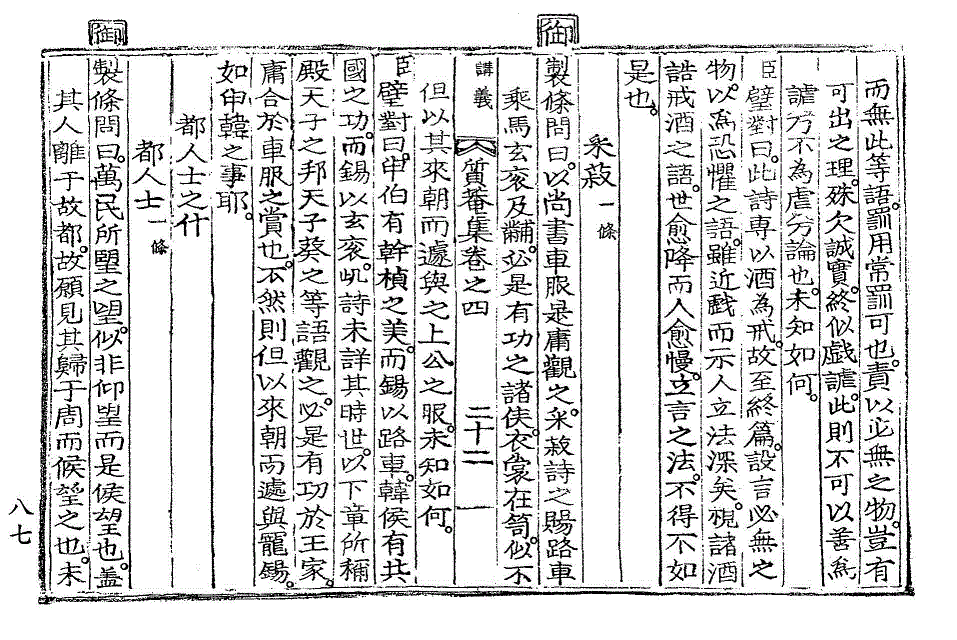 而无此等语。罚用常罚可也。责以必无之物。岂有可出之理。殊欠诚实。终似戏谑。此则不可以善为谑兮不为虐兮论也。未知如何。
而无此等语。罚用常罚可也。责以必无之物。岂有可出之理。殊欠诚实。终似戏谑。此则不可以善为谑兮不为虐兮论也。未知如何。臣璧对曰。此诗专以酒为戒。故至终篇。设言必无之物。以为恐惧之语。虽近戏而示人立法深矣。视诸酒诰戒酒之语。世愈降而人愈慢。立言之法。不得不如是也。
采菽(一条)
御制条问曰。以尚书车服是庸观之。采菽诗之赐路车乘马玄衮及黼。必是有功之诸侯。衣裳在笥。似不但以其来朝而遽与之上公之服。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申伯有干桢之美。而锡以路车。韩侯有共国之功。而锡以玄衮。此诗未详其时世。以下章所称殿天子之邦天子葵之等语观之。必是有功于王家。庸合于车服之赏也。不然则但以来朝而遽与宠锡。如申韩之事耶。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一条)
御制条问曰。万民所望之望。似非仰望而是候望也。盖其人离于故都。故愿见其归于周而候望之也。未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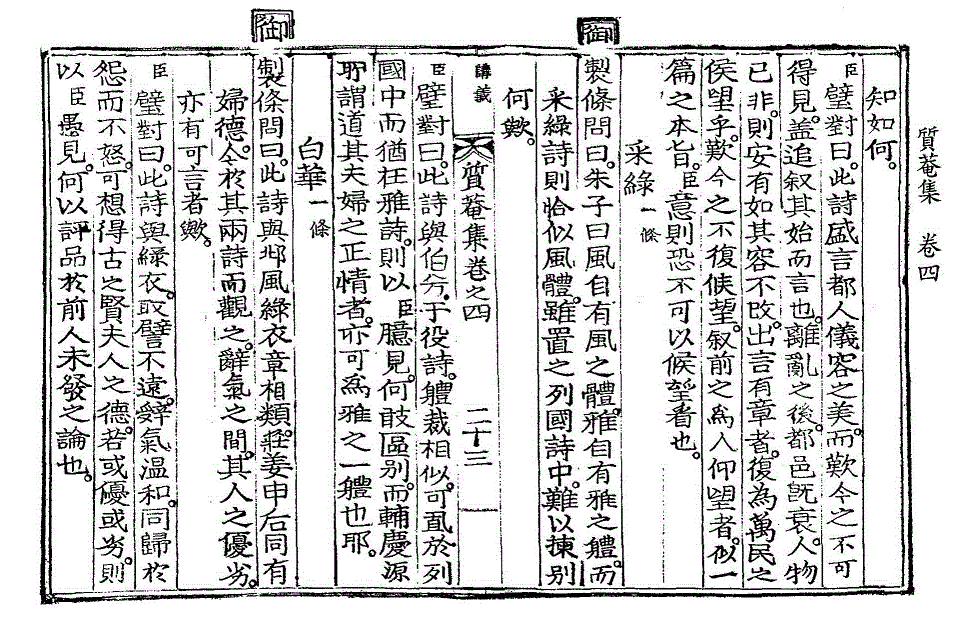 知如何。
知如何。臣璧对曰。此诗盛言都人仪容之美。而叹今之不可得见。盖追叙其始而言也。离乱之后。都邑既衰。人物已非。则安有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者。复为万民之候望乎。叹今之不复候望。叙前之为人仰望者。似一篇之本旨。臣意则恐不可以候望看也。
采绿(一条)
御制条问曰。朱子曰风自有风之体。雅自有雅之体。而采绿诗则恰似风体。虽置之列国诗中。难以拣别何欤。
臣璧对曰。此诗与伯兮,于役诗。体裁相似。可置于列国中而犹在雅诗。则以臣臆见。何敢区别。而辅庆源所谓道其夫妇之正情者。亦可为雅之一体也耶。
白华(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与邶风绿衣章相类。庄姜申后同有妇德。今于其两诗而观之。辞气之间。其人之优劣。亦有可言者欤。
臣璧对曰。此诗与绿衣。取譬不远。辞气温和。同归于怨而不怒。可想得古之贤夫人之德。若或优或劣。则以臣愚见。何以评品于前人未发之论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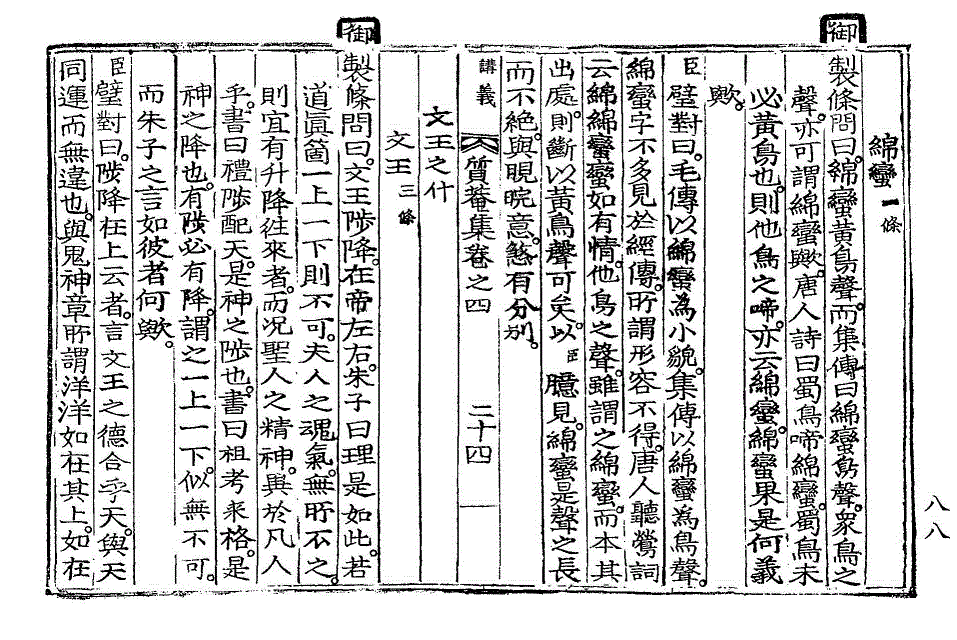 绵蛮(一条)
绵蛮(一条)御制条问曰。绵蛮黄鸟声。而集传曰绵蛮鸟声。众鸟之声。亦可谓绵蛮欤。唐人诗曰蜀鸟啼绵蛮。蜀鸟未必黄鸟也。则他鸟之啼。亦云绵蛮。绵蛮果是何义欤。
臣璧对曰。毛传以绵蛮为小貌。集传以绵蛮为鸟声。绵蛮字不多见于经传。所谓形容不得。唐人听莺词云绵绵蛮蛮如有情。他鸟之声。虽谓之绵蛮。而本其出处。则断以黄鸟声可矣。以臣臆见。绵蛮是声之长而不绝。与睍皖意。煞有分别。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三条)
御制条问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子曰理是如此。若道真个一上一下则不可。夫人之魂气。无所不之。则宜有升降往来者。而况圣人之精神。异于凡人乎。书曰礼陟配天。是神之陟也。书曰祖考来格。是神之降也。有陟必有降。谓之一上一下。似无不可。而朱子之言如彼者何欤。
臣璧对曰。陟降在上云者。言文王之德合乎天。与天同运而无违也。与鬼神章所谓洋洋如在其上。如在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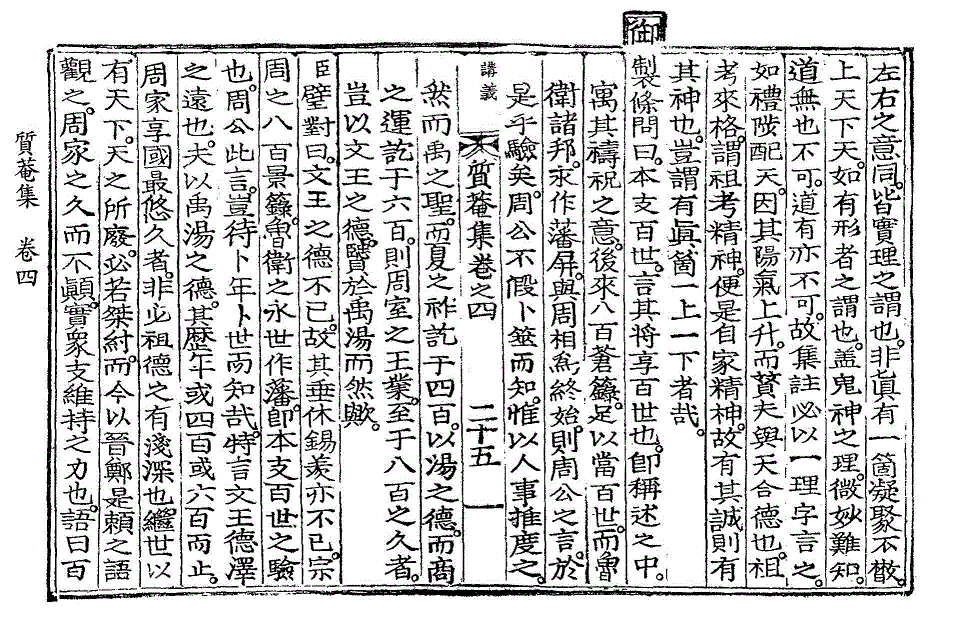 左右之意同。皆实理之谓也。非真有一个凝聚不散。上天下天。如有形者之谓也。盖鬼神之理。微妙难知。道无也不可。道有亦不可。故集注必以一理字言之。如礼陟配天。因其阳气上升。而赞夫与天合德也。祖考来格。谓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有其诚则有其神也。岂谓有真个一上一下者哉。
左右之意同。皆实理之谓也。非真有一个凝聚不散。上天下天。如有形者之谓也。盖鬼神之理。微妙难知。道无也不可。道有亦不可。故集注必以一理字言之。如礼陟配天。因其阳气上升。而赞夫与天合德也。祖考来格。谓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有其诚则有其神也。岂谓有真个一上一下者哉。御制条问曰。本支百世。言其将享百世也。即称述之中。寓其祷祝之意。后来八百苍箓。足以当百世。而鲁卫诸邦。永作藩屏。与周相为终始。则周公之言。于是乎验矣。周公不假卜筮而知。惟以人事推度之。然而禹之圣。而夏之祚讫于四百。以汤之德。而商之运讫于六百。则周室之王业。至于八百之久者。岂以文王之德。贤于禹汤而然欤。
臣璧对曰。文王之德不已。故其垂休锡羡亦不已。宗周之八百景箓。鲁卫之永世作藩。即本支百世之验也。周公此言。岂待卜年卜世而知哉。特言文王德泽之远也。夫以禹汤之德。其历年或四百或六百而止。周家享国最悠久者。非必祖德之有浅深也继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而今以晋郑是赖之语观之。周家之久而不颠。实众支维持之力也。语曰百
质庵集卷之四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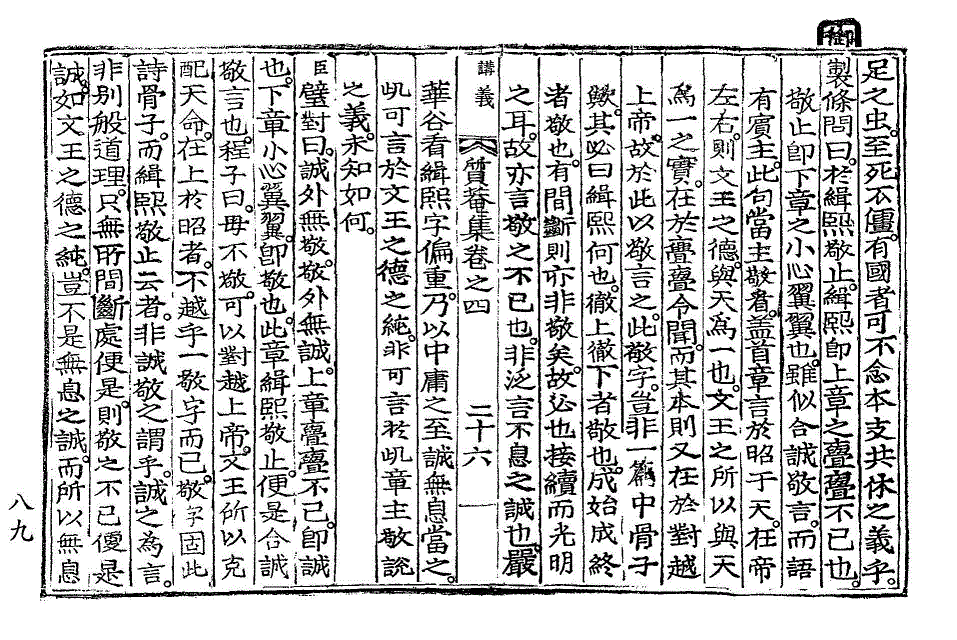 足之虫。至死不僵。有国者可不念本支共休之义乎。
足之虫。至死不僵。有国者可不念本支共休之义乎。御制条问曰。于缉熙敬止。缉熙即上章之亹亹不已也。敬止即下章之小心翼翼也。虽似合诚敬言。而语有宾主。此句当主敬看。盖首章言于昭于天。在帝左右。则文王之德。与天为一也。文王之所以与天为一之实。在于亹亹令闻。而其本则又在于对越上帝。故于此以敬言之。此敬字。岂非一篇中骨子欤。其必曰缉熙何也。彻上彻下者敬也。成始成终者敬也。有间断则亦非敬矣。故必也接续而光明之耳。故亦言敬之不已也。非泛言不息之诚也。严华谷看缉熙字偏重。乃以中庸之至诚无息当之。此可言于文王之德之纯。非可言于此章主敬说之义。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诚外无敬。敬外无诚。上章亹亹不已。即诚也。下章小心翼翼。即敬也。此章缉熙敬止。便是合诚敬言也。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文王所以克配天命。在上于昭者。不越乎一敬字而已。敬字固此诗骨子。而缉熙敬止云者。非诚敬之谓乎。诚之为言。非别般道理。只无所间断处便是。则敬之不已便是诚。如文王之德之纯。岂不是无息之诚。而所以无息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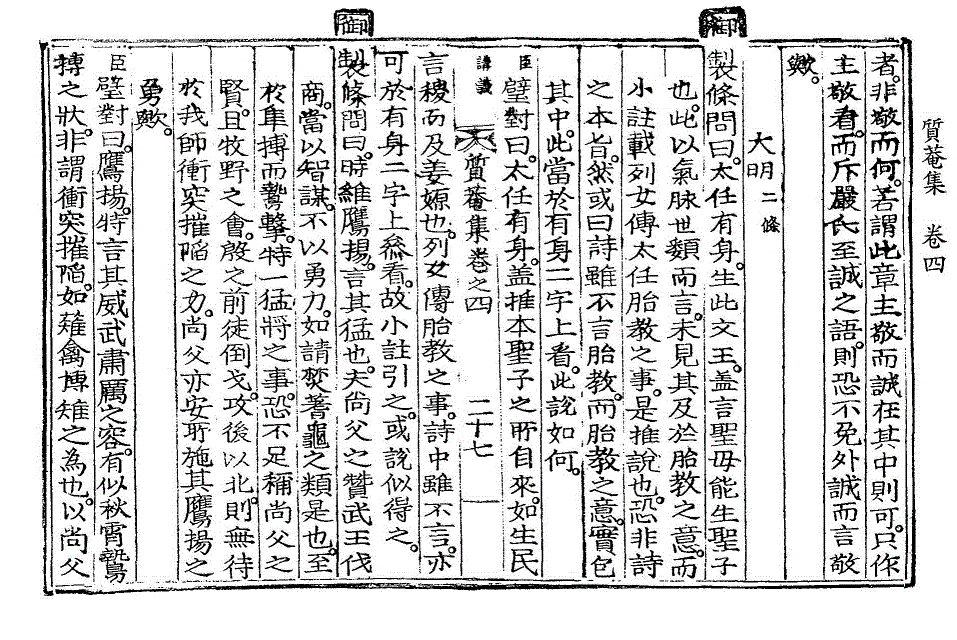 者。非敬而何。若谓此章主敬而诚在其中则可。只作主敬看。而斥严氏至诚之语。则恐不免外诚而言敬欤。
者。非敬而何。若谓此章主敬而诚在其中则可。只作主敬看。而斥严氏至诚之语。则恐不免外诚而言敬欤。大明(二条)
御制条问曰。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盖言圣母能生圣子也。此以气脉世类而言。未见其及于胎教之意。而小注载列女传太任胎教之事。是推说也。恐非诗之本旨。然或曰诗虽不言胎教。而胎教之意。实包其中。此当于有身二字上看。此说如何。
臣璧对曰。太任有身。盖推本圣子之所自来。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也。列女传胎教之事。诗中虽不言。亦可于有身二字上参看。故小注引之。或说似得之。
御制条问曰。时维鹰扬。言其猛也。夫尚父之赞武王伐商。当以智谋。不以勇力。如请焚蓍龟之类是也。至于隼搏而鸷击。特一猛将之事。恐不足称尚父之贤。且牧野之会。殷之前徒倒戈。攻后以北。则无待于我师冲突摧陷之力。尚父亦安所施其鹰扬之勇欤。
臣璧对曰。鹰扬。特言其威武肃厉之容。有似秋霄鸷搏之状。非谓冲突摧陷。如薙禽搏雉之为也。以尚父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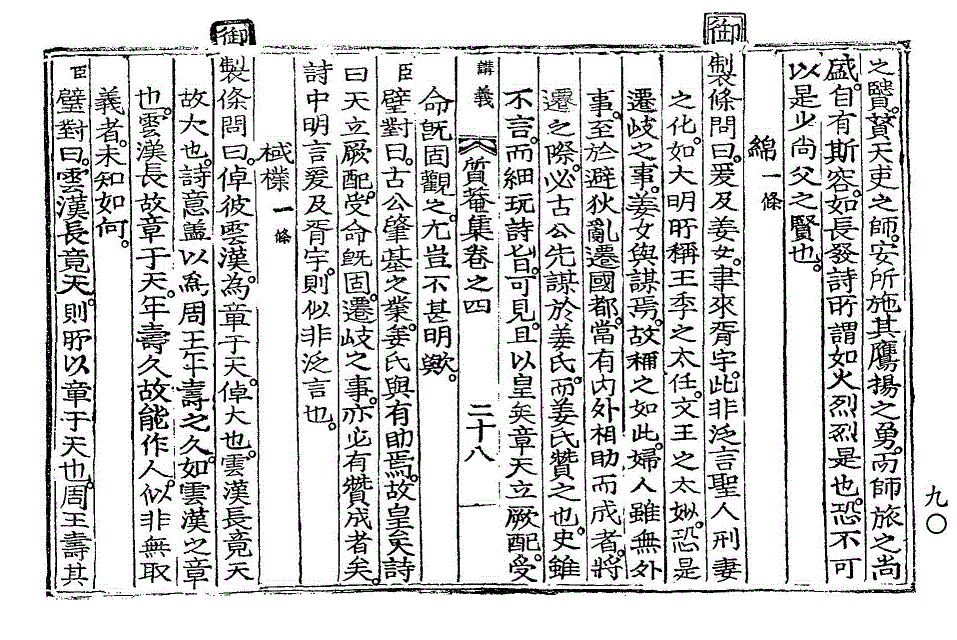 之贤。赞天吏之师。安所施其鹰扬之勇。而师旅之尚盛。自有斯容。如长发诗所谓如火烈烈是也。恐不可以是少尚父之贤也。
之贤。赞天吏之师。安所施其鹰扬之勇。而师旅之尚盛。自有斯容。如长发诗所谓如火烈烈是也。恐不可以是少尚父之贤也。绵(一条)
御制条问曰。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此非泛言圣人刑妻之化。如大明所称王季之太任。文王之太姒。恐是迁岐之事。姜女与谋焉。故称之如此。妇人虽无外事。至于避狄乱迁国都。当有内外相助而成者。将迁之际。必古公先谋于姜氏。而姜氏赞之也。史虽不言。而细玩诗旨。可见。且以皇矣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观之。尤岂不甚明欤。
臣璧对曰。古公肇基之业。姜氏与有助焉。故皇矣诗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迁岐之事。亦必有赞成者矣。诗中明言爰及胥宇。则似非泛言也。
棫朴(一条)
御制条问曰。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倬大也。云汉长竟天故大也。诗意盖以为周王年寿之久。如云汉之章也。云汉长故章于天。年寿久故能作人。似非无取义者。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云汉长竟天。则所以章于天也。周王寿其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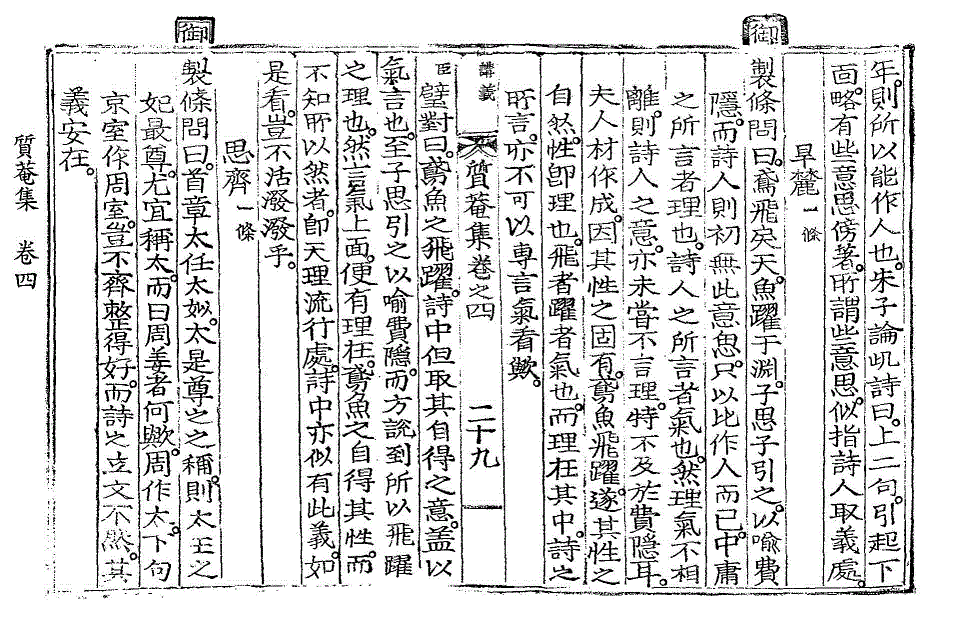 年。则所以能作人也。朱子论此诗曰。上二句。引起下面。略有些意思傍著。所谓些意思。似指诗人取义处。
年。则所以能作人也。朱子论此诗曰。上二句。引起下面。略有些意思傍著。所谓些意思。似指诗人取义处。旱麓(一条)
御制条问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子思子引之。以喻费隐。而诗人则初无此意思。只以比作人而已。中庸之所言者理也。诗人之所言者气也。然理气不相离。则诗人之意。亦未尝不言理。特不及于费隐耳。夫人材作成。因其性之固有。鸢鱼飞跃。遂其性之自然。性即理也。飞者跃者气也。而理在其中。诗之所言。亦不可以专言气看欤。
臣璧对曰。鸢鱼之飞跃。诗中但取其自得之意。盖以气言也。至子思引之以喻费隐。而方说到所以飞跃之理也。然言气上面。便有理在。鸢鱼之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者。即天理流行处。诗中亦似有此义。如是看。岂不活泼泼乎。
思齐(一条)
御制条问曰。首章太任太姒。太是尊之之称。则太王之妃最尊。尤宜称太。而曰周姜者何欤。周作太。下句京室作周室。岂不齐整得好。而诗之立文不然。其义安在。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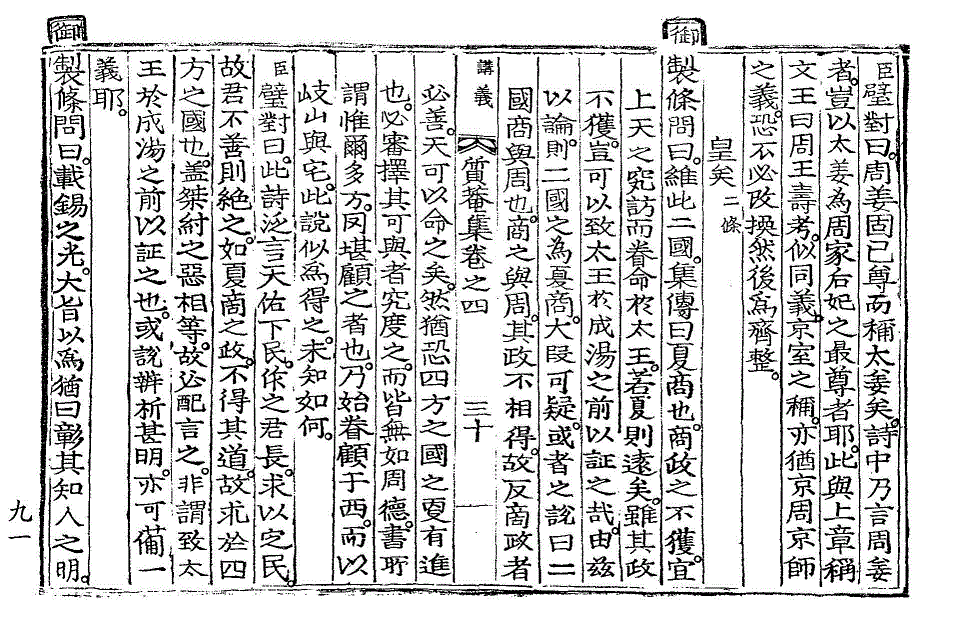 臣璧对曰。周姜固已尊而称太姜矣。诗中乃言周姜者。岂以太姜为周家后妃之最尊者耶。此与上章称文王曰周王寿考。似同义。京室之称。亦犹京周京师之义。恐不必改换然后为齐整。
臣璧对曰。周姜固已尊而称太姜矣。诗中乃言周姜者。岂以太姜为周家后妃之最尊者耶。此与上章称文王曰周王寿考。似同义。京室之称。亦犹京周京师之义。恐不必改换然后为齐整。皇矣(二条)
御制条问曰。维此二国。集传曰夏商也。商政之不获。宜上天之究访而眷命于太王。若夏则远矣。虽其政不获。岂可以致太王于成汤之前以证之哉。由玆以论。则二国之为夏商。大段可疑。或者之说曰二国商与周也。商之与周。其政不相得。故反商政者必善。天可以命之矣。然犹恐四方之国之更有进也。必审择其可与者究度之。而皆无如周德。书所谓惟尔多方。罔堪顾之者也。乃始眷顾于西。而以岐山与宅。此说似为得之。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诗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长。求以定民。故君不善则绝之。如夏商之政。不得其道。故求于四方之国也。盖桀纣之恶相等。故必配言之。非谓致太王于成汤之前以证之也。或说辨析甚明。亦可备一义耶。
御制条问曰。载锡之光。大旨以为犹曰彰其知人之明。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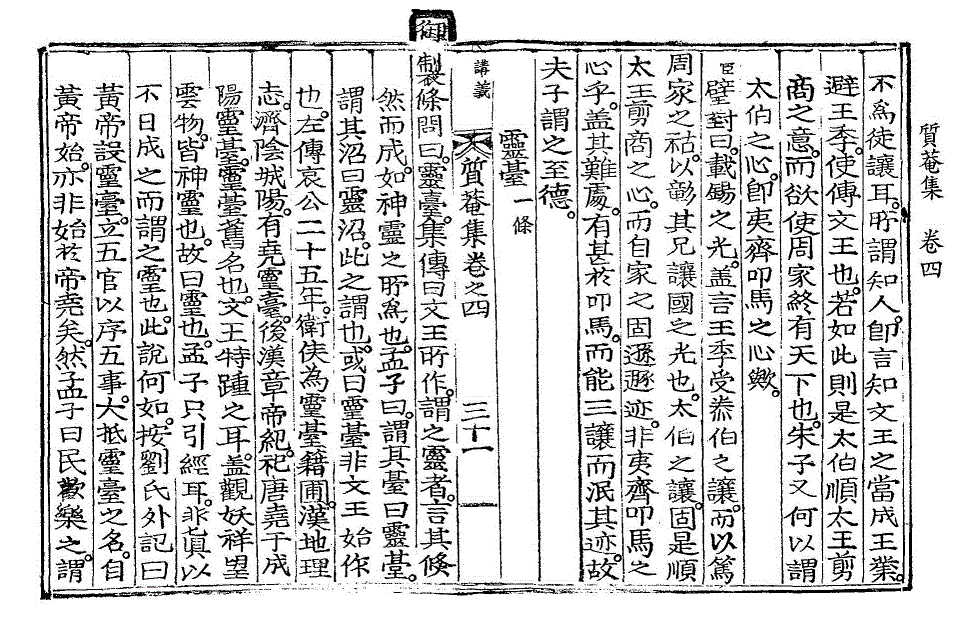 不为徒让耳。所谓知人。即言知文王之当成王业。避王季。使传文王也。若如此则是太伯顺太王剪商之意。而欲使周家终有天下也。朱子又何以谓太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欤。
不为徒让耳。所谓知人。即言知文王之当成王业。避王季。使传文王也。若如此则是太伯顺太王剪商之意。而欲使周家终有天下也。朱子又何以谓太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欤。臣璧对曰。载锡之光。盖言王季受泰伯之让。而以笃周家之祜。以彰其兄让国之光也。太伯之让。固是顺太王剪商之心。而自家之固逊遁迹。非夷齐叩马之心乎。盖其难处。有甚于叩马。而能三让而泯其迹。故夫子谓之至德。
灵台(一条)
御制条问曰。灵台。集传曰文王所作。谓之灵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孟子曰。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此之谓也。或曰灵台非文王始作也。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为灵台籍圃。汉地理志。济阴城阳。有尧灵台。后汉章帝纪。祀唐尧于成阳灵台。灵台旧名也。文王特踵之耳。盖观妖祥望云物。皆神灵也。故曰灵也。孟子只引经耳。非真以不日成之而谓之灵也。此说何如。按刘氏外记曰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序五事。大抵灵台之名。自黄帝始。亦非始于帝尧矣。然孟子曰民欢乐之。谓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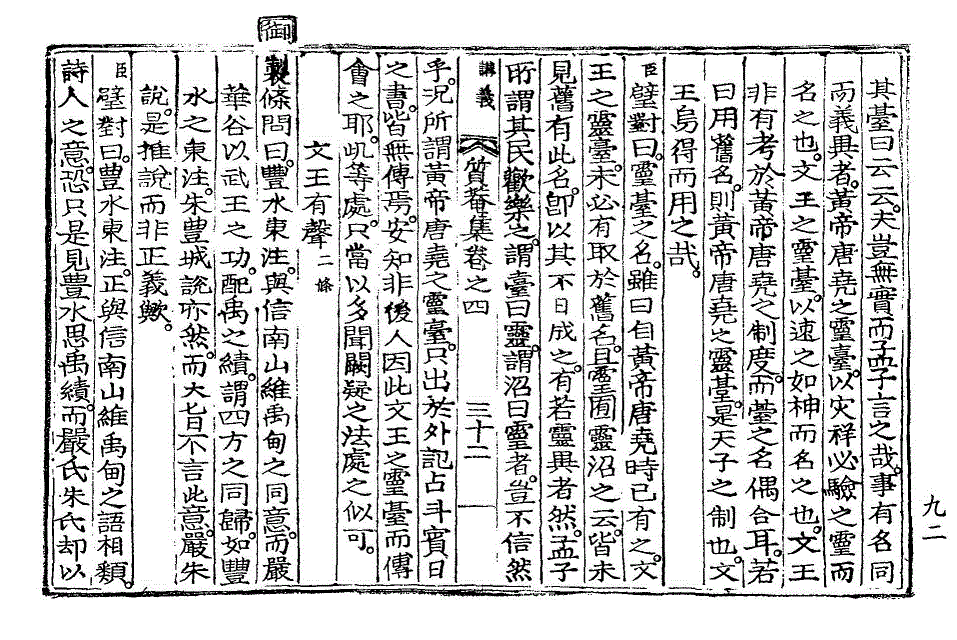 其台曰云云。夫岂无实而孟子言之哉。事有名同而义异者。黄帝唐尧之灵台。以灾祥必验之灵而名之也。文王之灵台。以速之如神而名之也。文王非有考于黄帝唐尧之制度。而台之名偶合耳。若曰用旧名。则黄帝唐尧之灵台。是天子之制也。文王乌得而用之哉。
其台曰云云。夫岂无实而孟子言之哉。事有名同而义异者。黄帝唐尧之灵台。以灾祥必验之灵而名之也。文王之灵台。以速之如神而名之也。文王非有考于黄帝唐尧之制度。而台之名偶合耳。若曰用旧名。则黄帝唐尧之灵台。是天子之制也。文王乌得而用之哉。臣璧对曰。灵台之名。虽曰自黄帝唐尧时已有之。文王之灵台。未必有取于旧名。且灵囿灵沼之云。皆未见旧有此名。即以其不日成之。有若灵异者然。孟子所谓其民欢乐之。谓台曰灵。谓沼曰灵者。岂不信然乎。况所谓黄帝唐尧之灵台。只出于外记占斗宾日之书。皆无传焉。安知非后人因此文王之灵台而傅会之耶。此等处。只当以多闻阙疑之法处之似可。
文王有声(二条)
御制条问曰。丰水东注。与信南山维禹甸之同意。而严华谷以武王之功。配禹之绩。谓四方之同归。如丰水之东注。朱礼城说亦然。而大旨不言此意。严朱说。是推说而非正义欤。
臣璧对曰。礼水东注。正与信南山维禹甸之语相类。诗人之意。恐只是见礼水思禹绩。而严氏朱氏却以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3H 页
 四方攸同。比丰水东注。而谓武王之功。配禹无愧。推说得尽好。然解经之法。宁浅毋深。宁拙毋巧。则大旨不以此意言之者。恐以此。
四方攸同。比丰水东注。而谓武王之功。配禹无愧。推说得尽好。然解经之法。宁浅毋深。宁拙毋巧。则大旨不以此意言之者。恐以此。御制条问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大旨曰此言武王徙居镐京。讲学行礼。而天下自服。然则未徙镐作辟雍之前。天下犹有未尽心服者欤。书之武成曰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则天下之心服。于此已见矣。何待于辟雍之讲学行礼而后。始皆心服欤。
臣璧对曰。善政之服民。未若善教之服民心。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善政也。徙镐作雍。讲学行礼。善教也。四方之服周。非不久矣。其心悦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则必待善教之入人深。王者服民心之道。可不以兴学校为先务乎。
生民之什
生民(一条)
御制条问曰。履帝武敏。集传曰武迹。敏拇。夫巨迹之说。以玄鸟之生商。泽龙之兴汉推之。固不可谓无是理。然以大人之迹而谓上帝之拇。则易以致惑。盖大人是鬼神。鬼神固有现形者。故留其迹矣。帝以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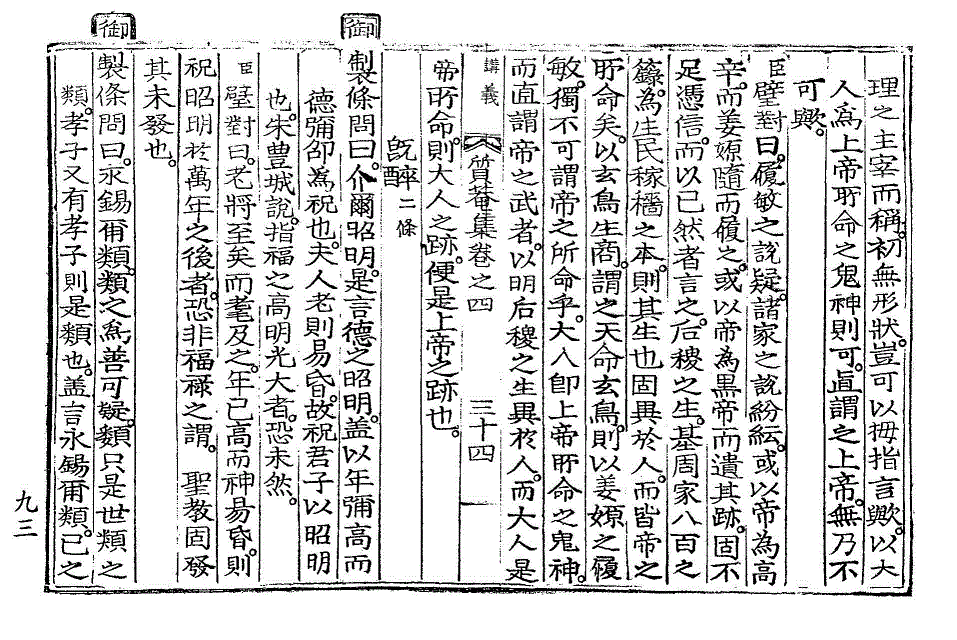 理之主宰而称。初无形状。岂可以拇指言欤。以大人为上帝所命之鬼神则可。直谓之上帝。无乃不可欤。
理之主宰而称。初无形状。岂可以拇指言欤。以大人为上帝所命之鬼神则可。直谓之上帝。无乃不可欤。臣璧对曰。履敏之说疑。诸家之说纷纭。或以帝为高辛。而姜嫄随而履之。或以帝为黑帝而遗其迹。固不足凭信。而以已然者言之。后稷之生。基周家八百之箓。为生民稼穑之本。则其生也固异于人。而皆帝之所命矣。以玄鸟生商。谓之天命玄鸟。则以姜嫄之履敏。独不可谓帝之所命乎。大人即上帝所命之鬼神。而直谓帝之武者。以明后稷之生异于人。而大人是帝所命。则大人之迹。便是上帝之迹也。
既醉(二条)
御制条问曰。介尔昭明。是言德之昭明。盖以年弥高而德弥卲为祝也。夫人老则易昏。故祝君子以昭明也。朱礼城说。指福之高明光大者。恐未然。
臣璧对曰。老将至矣而耄及之。年已高而神易昏。则祝昭明于万年之后者。恐非福禄之谓。 圣教固发其未发也。
御制条问曰。永锡尔类。类之为善可疑。类只是世类之类。孝子又有孝子则是类也。盖言永锡尔类。己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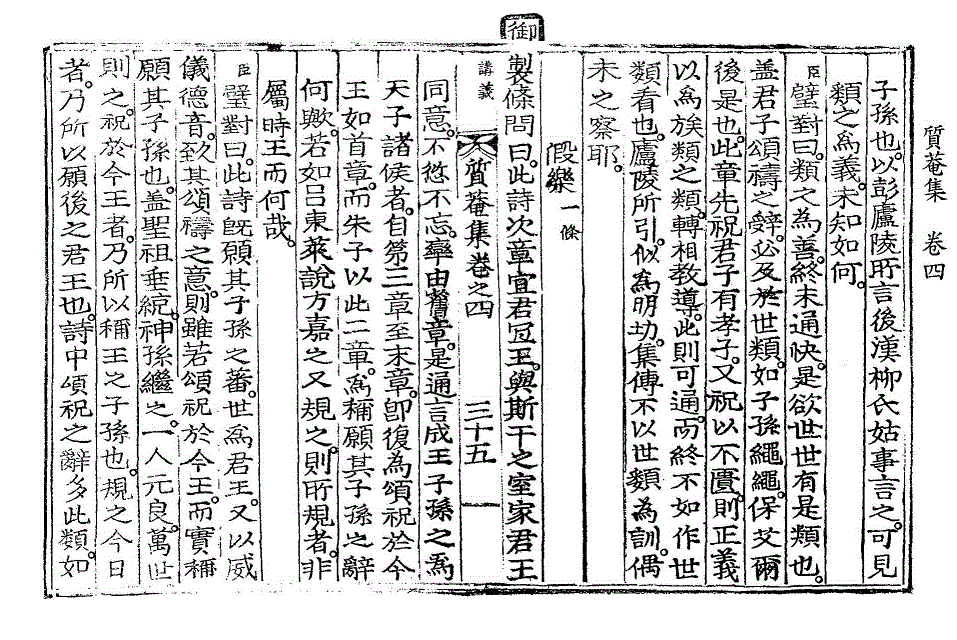 子孙也。以彭庐陵所言后汉柳氏姑事言之。可见类之为义。未知如何。
子孙也。以彭庐陵所言后汉柳氏姑事言之。可见类之为义。未知如何。臣璧对曰。类之为善。终未通快。是欲世世有是类也。盖君子颂祷之辞。必及于世类。如子孙绳绳。保艾尔后是也。此章先祝君子有孝子。又祝以不匮。则正义以为族类之类。转相教导。此则可通。而终不如作世类看也。庐陵所引。似为明切。集传不以世类为训。偶未之察耶。
假乐(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次章宜君宜王。与斯干之室家君王同意。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通言成王子孙之为天子诸侯者。自第三章至末章。即复为颂祝于今王如首章。而朱子以此二章。为称愿其子孙之辞何欤。若如吕东莱说方嘉之又规之。则所规者。非属时王而何哉。
臣璧对曰。此诗既愿其子孙之蕃。世为君王。又以威仪德音。致其颂祷之意。则虽若颂祝于今王。而实称愿其子孙也。盖圣祖垂统。神孙继之。一人元良。万世则之。祝于今王者。乃所以称王之子孙也。规之今日者。乃所以愿后之君王也。诗中颂祝之辞多此类。如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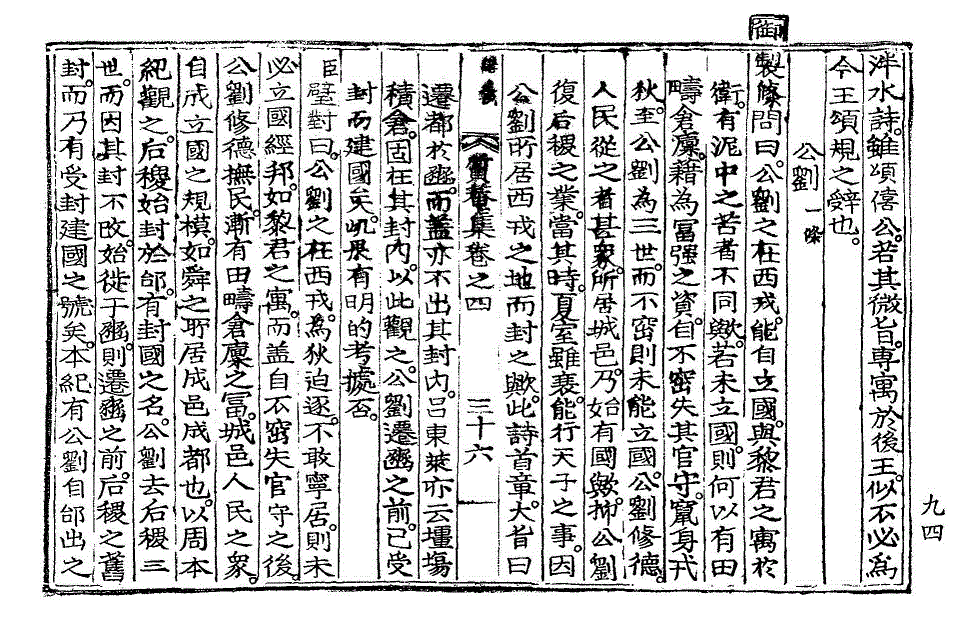 泮水诗。虽颂僖公。若其微旨。专寓于后王。似不必为今王颂规之辞也。
泮水诗。虽颂僖公。若其微旨。专寓于后王。似不必为今王颂规之辞也。公刘(一条)
御制条问曰。公刘之在西戎。能自立国。与黎君之寓于卫。有泥中之苦者不同欤。若未立国。则何以有田畴仓廪。藉为富强之资。自不窋失其官守。窜身戎狄。至公刘为三世。而不窋则未能立国。公刘修德。人民从之者甚众。所居城邑。乃始有国欤。抑公刘复后稷之业。当其时。夏室虽衰。能行天子之事。因公刘所居西戎之地而封之欤。此诗首章。大旨曰迁都于豳。而盖亦不出其封内。吕东莱亦云疆场积仓。固在其封内。以此观之。公刘迁豳之前。已受封而建国矣。此果有明的考据否。
臣璧对曰。公刘之在西戎。为狄迫逐。不敢宁居。则未必立国经邦。如黎君之寓。而盖自不窋失官守之后。公刘修德抚民。渐有田畴仓廪之富。城邑人民之众。自成立国之规模。如舜之所居成邑成都也。以周本纪观之。后稷始封于邰。有封国之名。公刘去后稷三世。而因其封不改。始徙于豳。则迁豳之前。后稷之旧封。而乃有受封建国之号矣。本纪有公刘自邰出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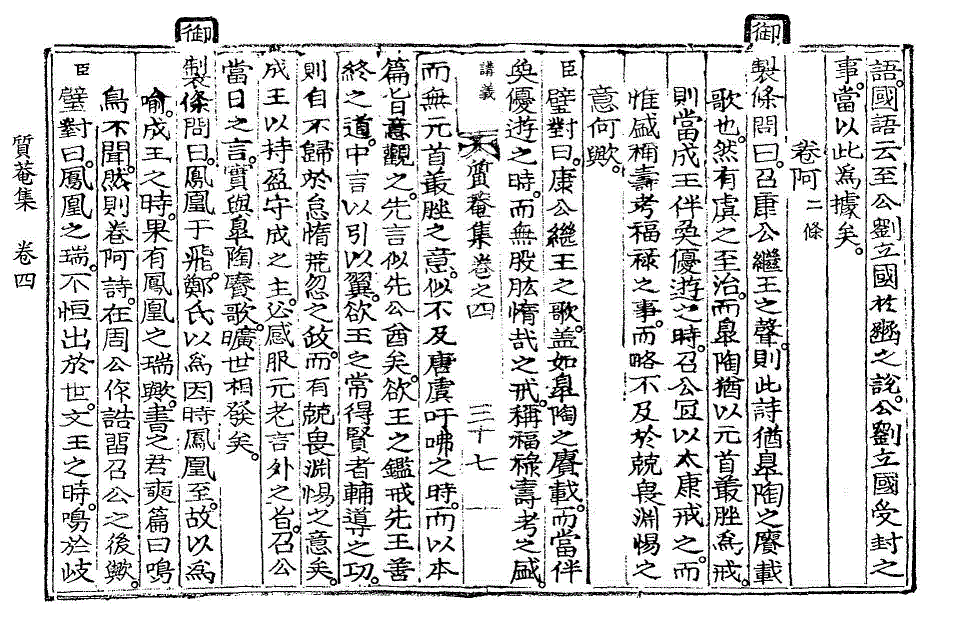 语。国语云至公刘立国于豳之说。公刘立国受封之事。当以此为据矣。
语。国语云至公刘立国于豳之说。公刘立国受封之事。当以此为据矣。卷阿(二条)
御制条问曰。召康公继王之声。则此诗犹皋陶之赓载歌也。然有虞之至治。而皋陶犹以元首丛脞为戒。则当成王伴奂优游之时。召公宜以太康戒之。而惟盛称寿考福禄之事。而略不及于兢畏渊惕之意何欤。
臣璧对曰。康公继王之歌。盖如皋陶之赓载。而当伴奂优游之时。而无股肱惰哉之戒。称福禄寿考之盛。而无元首丛脞之意。似不及唐虞吁咈之时。而以本篇旨意观之。先言似先公酋矣。欲王之鉴戒先王善终之道。中言以引以翼。欲王之常得贤者辅导之功。则自不归于怠惰荒忽之政。而有兢畏渊惕之意矣。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必感服元老言外之旨。召公当日之言。实与皋陶赓歌。旷世相发矣。
御制条问曰。凤凰于飞。郑氏以为因时凤凰至。故以为喻。成王之时。果有凤凰之瑞欤。书之君奭篇曰鸣鸟不闻。然则卷阿诗。在周公作诰留召公之后欤。
臣璧对曰。凤凰之瑞。不恒出于世。文王之时。鸣于岐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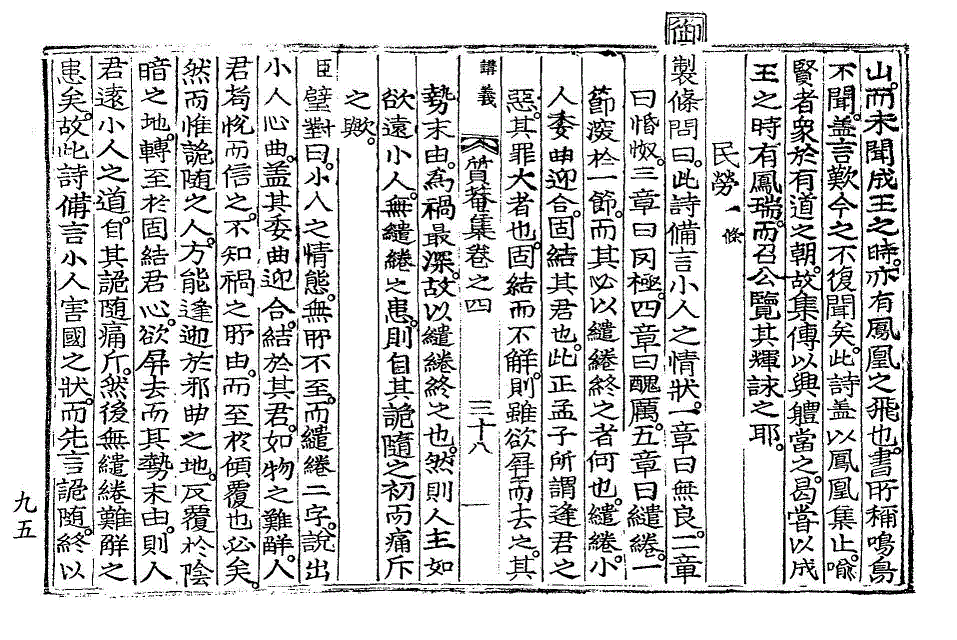 山。而未闻成王之时。亦有凤凰之飞也。书所称鸣鸟不闻。盖言叹今之不复闻矣。此诗盖以凤凰集止。喻贤者众于有道之朝。故集传以兴体当之。曷尝以成王之时有凤瑞。而召公览其辉咏之耶。
山。而未闻成王之时。亦有凤凰之飞也。书所称鸣鸟不闻。盖言叹今之不复闻矣。此诗盖以凤凰集止。喻贤者众于有道之朝。故集传以兴体当之。曷尝以成王之时有凤瑞。而召公览其辉咏之耶。民劳(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备言小人之情状。一章曰无良。二章曰惛怓。三章曰罔极。四章曰丑厉。五章曰缱绻。一节深于一节。而其必以缱绻终之者何也。缱绻。小人委曲迎合。固结其君也。此正孟子所谓逢君之恶。其罪大者也。固结而不解。则虽欲屏而去之。其势末由。为祸最深。故以缱绻终之也。然则人主如欲远小人。无缱绻之患。则自其诡随之初而痛斥之欤。
臣璧对曰。小人之情态。无所不至。而缱绻二字。说出小人心曲。盖其委曲迎合。结于其君。如物之难解。人君苟悦而信之。不知祸之所由。而至于倾覆也必矣。然而惟诡随之人。方能逢迎于邪曲之地。反覆于阴暗之地。转至于固结君心。欲屏去而其势末由。则人君远小人之道。自其诡随痛斤。然后无缱绻难解之患矣。故此诗备言小人害国之状。而先言诡随。终以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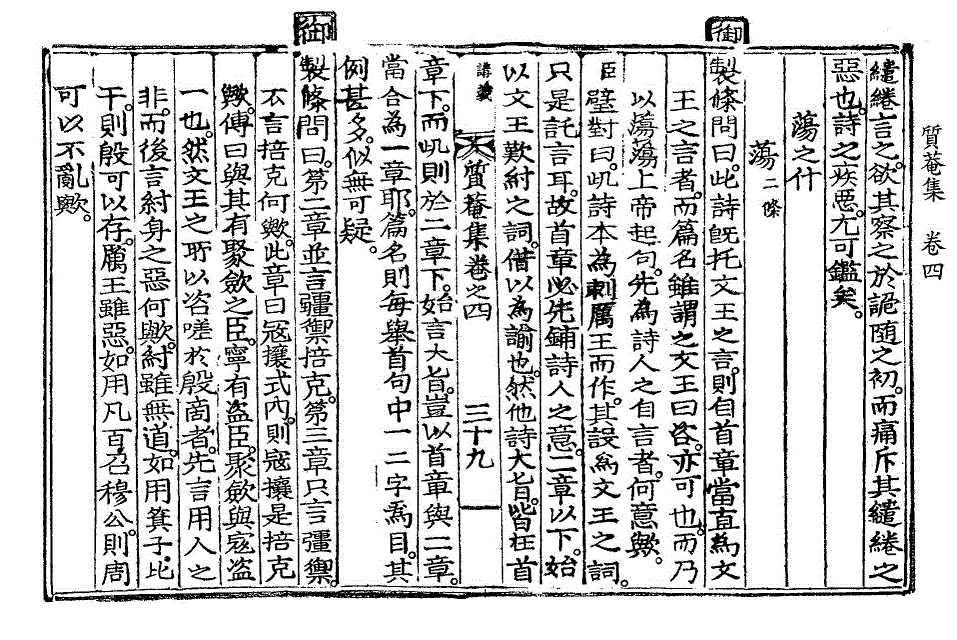 缱绻言之。欲其察之于诡随之初。而痛斥其缱绻之恶也。诗之疾恶。尤可鉴矣。
缱绻言之。欲其察之于诡随之初。而痛斥其缱绻之恶也。诗之疾恶。尤可鉴矣。荡之什
荡(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既托文王之言。则自首章当直为文王之言者。而篇名虽谓之文王曰咨。亦可也。而乃以荡荡上帝起句。先为诗人之自言者。何意欤。
臣璧对曰。此诗本为刺厉王而作。其设为文王之词。只是托言耳。故首章必先铺诗人之意。二章以下。始以文王叹纣之词。借以为谕也。然他诗大旨。皆在首章下。而此则于二章下。始言大旨。岂以首章与二章。当合为一章耶。篇名则每举首句中一二字为目。其例甚多。似无可疑。
御制条问曰。第二章并言疆御掊克。第三章只言彊御。不言掊克何欤。此章曰寇攘式内。则寇攘是掊克欤。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聚敛与寇盗一也。然文王之所以咨嗟于殷商者。先言用人之非。而后言纣身之恶何欤。纣虽无道。如用箕子,比干。则殷可以存。厉王虽恶。如用凡百,召穆公。则周可以不乱欤。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6L 页
 臣璧对曰。彊者彊梁。御如御人国门之御。则疆御掊克。皆是聚敛之臣。况寇攘式内之云。已深言掊克之害。则二章三章所言。可谓节节相应矣。盗臣与聚敛。有一于斯。已足以乱国。况兼之乎。然此㬥虐聚敛之臣。非其自为之。乃汝兴起此人而力为之。则其臣之恶。即纣之恶耳。先言用人之失者。岂非已言纣之恶者耶。噫。灵公之无道。而能用祝鮀,王孙贾。卫国赖以不丧。向使纣而能用箕子,比干。厉王而能用凡百,召穆公。岂不少补于危亡。而其如不能用何哉。
臣璧对曰。彊者彊梁。御如御人国门之御。则疆御掊克。皆是聚敛之臣。况寇攘式内之云。已深言掊克之害。则二章三章所言。可谓节节相应矣。盗臣与聚敛。有一于斯。已足以乱国。况兼之乎。然此㬥虐聚敛之臣。非其自为之。乃汝兴起此人而力为之。则其臣之恶。即纣之恶耳。先言用人之失者。岂非已言纣之恶者耶。噫。灵公之无道。而能用祝鮀,王孙贾。卫国赖以不丧。向使纣而能用箕子,比干。厉王而能用凡百,召穆公。岂不少补于危亡。而其如不能用何哉。抑(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旧说以为刺厉王。而考其时世不合。则又有追刺之说。朱子非之矣。既有朱子定论。则今不必更为疑难。惟将此作卫武自警看。而反覆讽咏。密切体验。则于吾身心为有益。南容之三复白圭。只是佩慎言之戒而已。何尝理会到刺王自警之间之是非耶。读诗法。恐当如此。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诗国语之说。明有可据。旧注追刺厉王之云。朱子既非之。后之为诗者。固当惟师说是信。不必缠绕于他说矣。只看作卫武自警之诗。而反覆讽咏。密切体验。则其有益于身心上功夫大矣。是故南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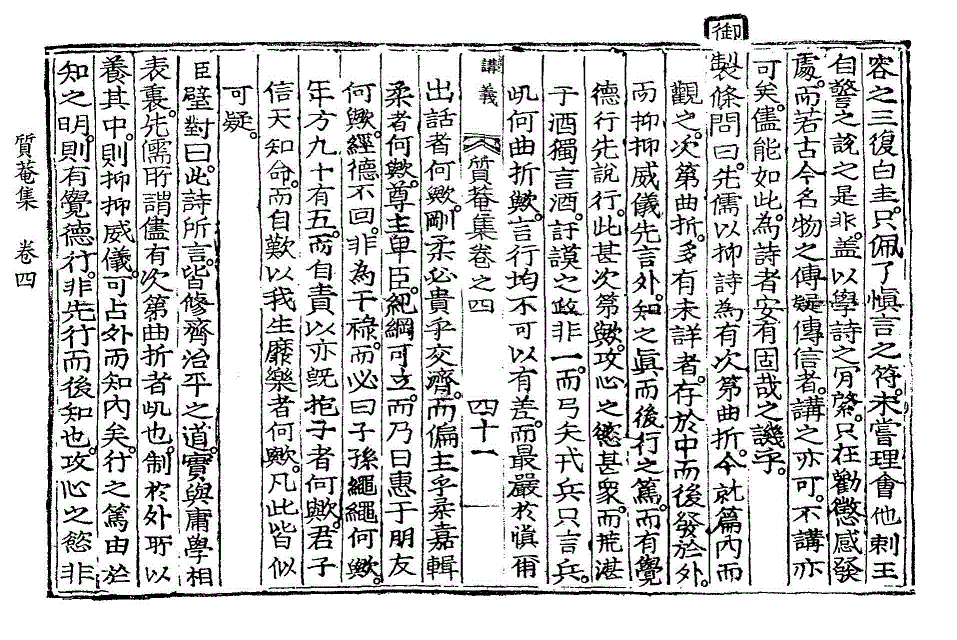 容之三复白圭。只佩了慎言之符。未尝理会他刺王自警之说之是非。盖以学诗之肯綮。只在劝惩感发处。而若古今名物之传疑传信者。讲之亦可。不讲亦可矣。尽能如此。为诗者安有固哉之讥乎。
容之三复白圭。只佩了慎言之符。未尝理会他刺王自警之说之是非。盖以学诗之肯綮。只在劝惩感发处。而若古今名物之传疑传信者。讲之亦可。不讲亦可矣。尽能如此。为诗者安有固哉之讥乎。御制条问曰。先儒以抑诗为有次第曲折。今就篇内而观之。次第曲折。多有未详者。存于中而后发于外。而抑抑威仪先言外。知之真而后行之笃。而有觉德行先说行。此甚次第欤。攻心之欲甚众。而荒湛于酒独言酒。吁谟之政非一。而弓矢戎兵只言兵。此何曲折欤。言行均不可以有差。而最严于慎尔出话者何欤。刚柔必贵乎交济。而偏主乎柔嘉辑柔者何欤。尊主卑臣。纪纲可立。而乃曰惠于朋友何欤。经德不回。非为干禄。而必曰子孙绳绳何欤。年方九十有五。而自责以亦既抱子者何欤。君子信天知命。而自叹以我生靡乐者何欤。凡此皆似可疑。
臣璧对曰。此诗所言。皆修齐治平之道。实与庸学相表里。先儒所谓尽有次第曲折者此也。制于外所以养其中。则抑抑威仪。可占外而知内矣。行之笃由于知之明。则有觉德行。非先行而后知也。攻心之欲非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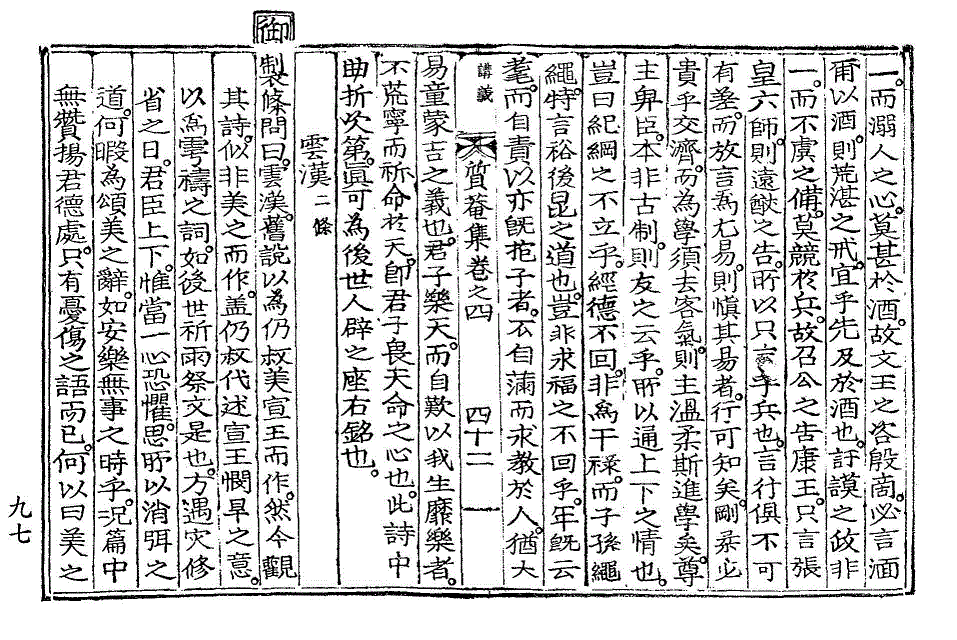 一。而溺人之心。莫甚于酒。故文王之咨殷商。必言湎尔以酒。则荒湛之戒。宜乎先及于酒也。吁谟之政非一。而不虞之备。莫竞于兵。故召公之告康王。只言张皇六师。则远猷之告。所以只言乎兵也。言行俱不可有差。而放言为尤易。则慎其易者。行可知矣。刚柔必贵乎交济。而为学须去客气。则主温柔斯进学矣。尊主卑臣。本非古制。则友之云乎。所以通上下之情也。岂曰纪纲之不立乎。经德不回。非为干禄。而子孙绳绳。特言裕后昆之道也。岂非求福之不回乎。年既云耄。而自责以亦既抱子者。不自满而求教于人。犹大易童蒙吉之义也。君子乐天。而自叹以我生靡乐者。不荒宁而祈命于天。即君子畏天命之心也。此诗中曲折次第。真可为后世人辟之座右铭也。
一。而溺人之心。莫甚于酒。故文王之咨殷商。必言湎尔以酒。则荒湛之戒。宜乎先及于酒也。吁谟之政非一。而不虞之备。莫竞于兵。故召公之告康王。只言张皇六师。则远猷之告。所以只言乎兵也。言行俱不可有差。而放言为尤易。则慎其易者。行可知矣。刚柔必贵乎交济。而为学须去客气。则主温柔斯进学矣。尊主卑臣。本非古制。则友之云乎。所以通上下之情也。岂曰纪纲之不立乎。经德不回。非为干禄。而子孙绳绳。特言裕后昆之道也。岂非求福之不回乎。年既云耄。而自责以亦既抱子者。不自满而求教于人。犹大易童蒙吉之义也。君子乐天。而自叹以我生靡乐者。不荒宁而祈命于天。即君子畏天命之心也。此诗中曲折次第。真可为后世人辟之座右铭也。云汉(二条)
御制条问曰。云汉。旧说以为仍叔美宣王而作。然今观其诗。似非美之而作。盖仍叔代述宣王悯旱之意。以为雩祷之词。如后世祈雨祭文是也。方遇灾修省之日。君臣上下。惟当一心恐惧。思所以消弭之道。何暇为颂美之辞。如安乐无事之时乎。况篇中无赞扬君德处。只有忧伤之语而已。何以曰美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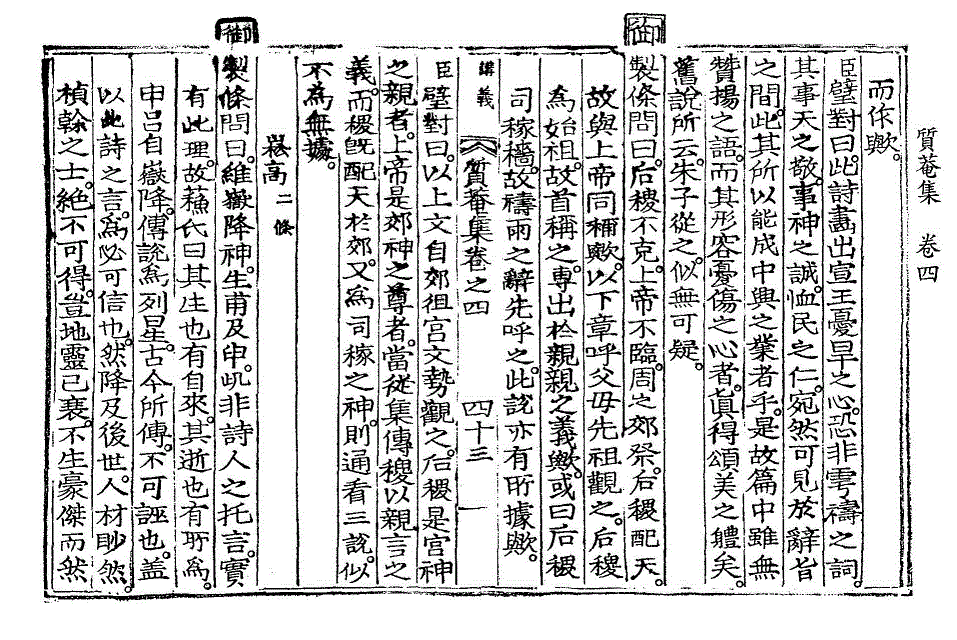 而作欤。
而作欤。臣璧对曰。此诗画出宣王忧旱之心。恐非雩祷之词。其事天之敬。事神之诚。恤民之仁。宛然可见于辞旨之间。此其所以能成中兴之业者乎。是故篇中虽无赞扬之语。而其形容忧伤之心者。真得颂美之体矣。旧说所云。朱子从之。似无可疑。
御制条问曰。后稷不克。上帝不临。周之郊祭。后稷配天。故与上帝同称欤。以下章呼父母先祖观之。后稷为始祖。故首称之。专出于亲亲之义欤。或曰后稷司稼穑。故祷雨之辞先呼之。此说亦有所据欤。
臣璧对曰。以上文自郊徂宫文势观之。后稷是宫神之亲者。上帝是郊神之尊者。当从集传稷以亲言之义。而稷既配天于郊。又为司稼之神。则通看三说。似不为无据。
崧高(二条)
御制条问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此非诗人之托言。实有此理。故苏氏曰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盖以此诗之言。为必可信也。然降及后世。人材眇然。桢干之士。绝不可得。岂地灵已衰。不生豪杰而然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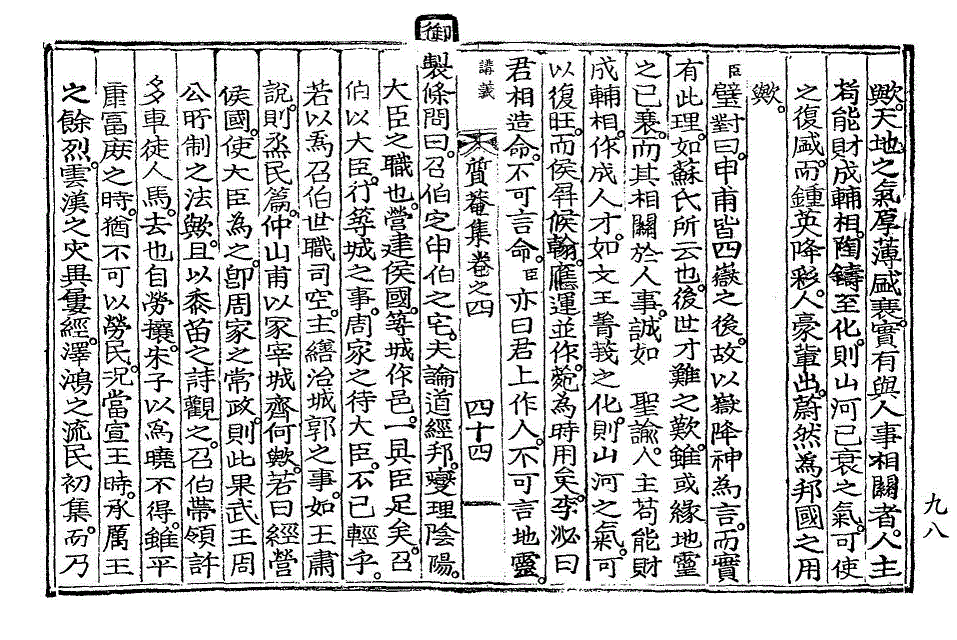 欤。天地之气厚薄盛衰。实有与人事相关者。人主苟能财成辅相。陶铸至化。则山河已衰之气。可使之复盛。而钟英降彩。人豪辈出。蔚然为邦国之用欤。
欤。天地之气厚薄盛衰。实有与人事相关者。人主苟能财成辅相。陶铸至化。则山河已衰之气。可使之复盛。而钟英降彩。人豪辈出。蔚然为邦国之用欤。臣璧对曰。申甫皆四岳之后。故以岳降神为言。而实有此理。如苏氏所云也。后世才难之叹。虽或缘地灵之已衰。而其相关于人事。诚如 圣谕。人主苟能财成辅相。作成人才。如文王菁莪之化。则山河之气。可以复旺。而候屏候翰。应运并作。菀为时用矣。李泌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臣亦曰君上作人。不可言地灵。
御制条问曰。召伯定申伯之宅。夫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大臣之职也。营建侯国。筑城作邑。一具臣足矣。召伯以大臣。行筑城之事。周家之待大臣。不已轻乎。若以为召伯世职司空。主缮治城郭之事。如王肃说。则烝民篇。仲山甫以冢宰城齐何欤。若曰经营侯国。使大臣为之。即周家之常政。则此果武王周公所制之法欤。且以黍苗之诗观之。召伯带领许多车徒人马。去也自劳攘。朱子以为晓不得。虽平康富庶之时。犹不可以劳民。况当宣王时。承厉王之馀烈。云汉之灾异屡经。泽鸿之流民初集。而乃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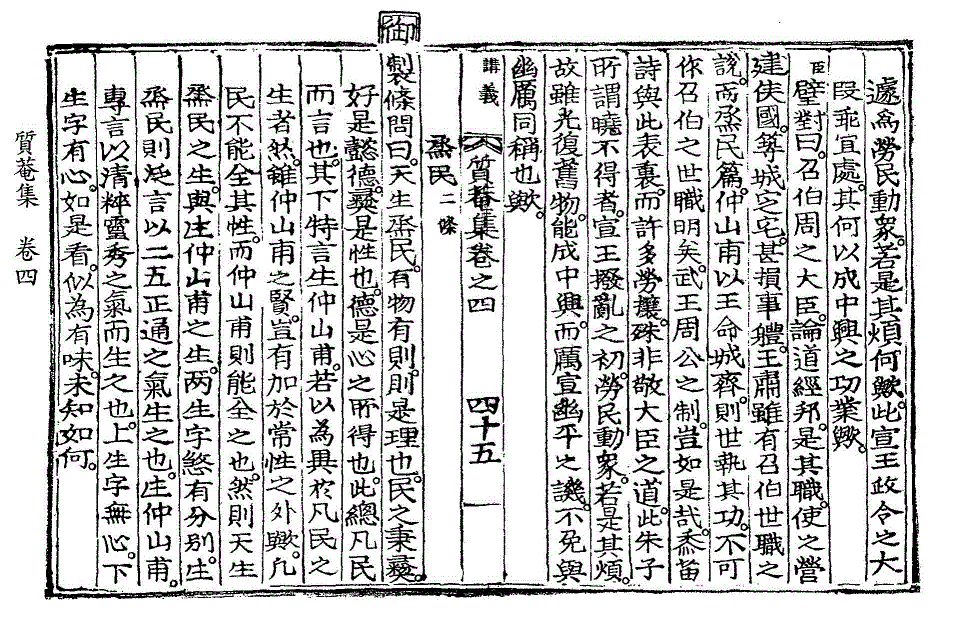 遽为劳民动众。若是其烦何欤。此宣王政令之大段乖宜处。其何以成中兴之功业欤。
遽为劳民动众。若是其烦何欤。此宣王政令之大段乖宜处。其何以成中兴之功业欤。臣璧对曰。召伯周之大臣。论道经邦。是其职。使之营建侯国。筑城定宅。甚损事体。王肃虽有召伯世职之说。而烝民篇。仲山甫以王命城齐。则世执其功。不可作召伯之世职明矣。武王周公之制。岂如是哉。黍苗诗与此表里。而许多劳攘。殊非敬大臣之道。此朱子所谓晓不得者。宣王拨乱之初。劳民动众。若是其烦。故虽光复旧物。能成中兴。而厉宣幽平之讥。不免与幽厉同称也欤。
烝民(二条)
御制条问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则是理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是性也。德是心之所得也。此总凡民而言也。其下特言生仲山甫。若以为异于凡民之生者然。虽仲山甫之贤。岂有加于常性之外欤。凡民不能全其性。而仲山甫则能全之也。然则天生烝民之生。与生仲山甫之生。两生字煞有分别。生烝民则泛言以二五正通之气生之也。生仲山甫。专言以清粹灵秀之气而生之也。上生字无心。下生字有心。如是看。似为有味。未知如何。
质庵集卷之四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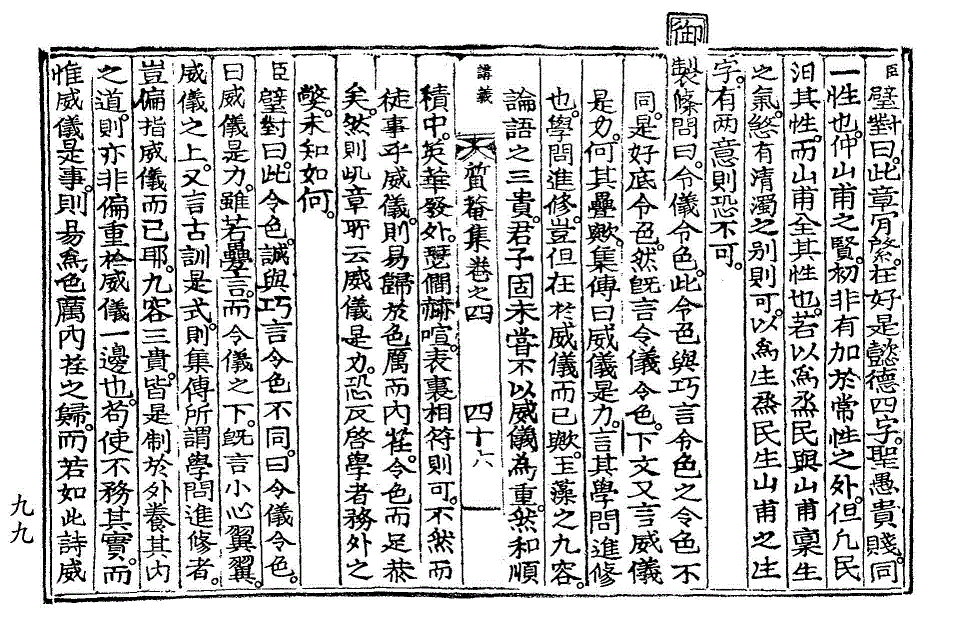 臣璧对曰。此章肯綮。在好是懿德四字。圣愚贵贱。同一性也。仲山甫之贤。初非有加于常性之外。但凡民汩其性。而山甫全其性也。若以为烝民与山甫禀生之气。煞有清浊之别则可。以为生烝民生山甫之生字。有两意则恐不可。
臣璧对曰。此章肯綮。在好是懿德四字。圣愚贵贱。同一性也。仲山甫之贤。初非有加于常性之外。但凡民汩其性。而山甫全其性也。若以为烝民与山甫禀生之气。煞有清浊之别则可。以为生烝民生山甫之生字。有两意则恐不可。御制条问曰。令仪令色。此令色与巧言令色之令色不同。是好底令色。然既言令仪令色。下文又言威仪是力。何其叠欤。集传曰威仪是力。言其学问进修也。学问进修。岂但在于威仪而已欤。玉藻之九容。论语之三贵。君子固未尝不以威仪为重。然和顺积中。英华发外。瑟僩赫喧。表里相符则可。不然而徒事乎威仪。则易归于色厉而内荏。令色而足恭矣。然则此章所云威仪是力。恐反启学者务外之㢢。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令色。诚与巧言令色不同。曰令仪令色。曰威仪是力。虽若叠言。而令仪之下。既言小心翼翼。威仪之上。又言古训是式。则集传所谓学问进修者。岂偏指威仪而已耶。九容三贵。皆是制于外养其内之道。则亦非偏重于威仪一边也。苟使不务其实。而惟威仪是事。则易为色厉内荏之归。而若如此诗威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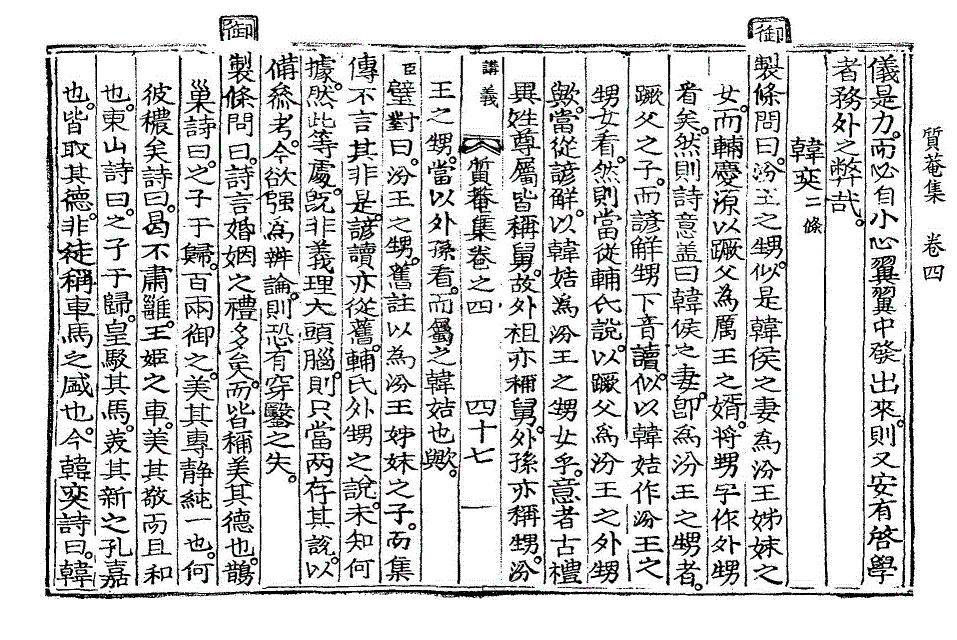 仪是力。而必自小心翼翼中发出来。则又安有启学者务外之弊哉。
仪是力。而必自小心翼翼中发出来。则又安有启学者务外之弊哉。韩奕(二条)
御制条问曰。汾王之甥。似是韩侯之妻为汾王姊妹之女。而辅庆源以蹶父为厉王之婿。将甥字作外甥看矣。然则诗意盖曰韩侯之妻。即为汾王之甥者。蹶父之子。而谚解甥下音读。似以韩姞作汾王之甥女看。然则当从辅氏说。以蹶父为汾王之外甥欤。当从谚解。以韩姞为汾王之甥女乎。意者古礼异姓尊属皆称舅。故外祖亦称舅。外孙亦称甥。汾王之甥。当以外孙看。而属之韩姞也欤。
臣璧对曰。汾王之甥。旧注以为汾王姊妹之子。而集传不言其非是。谚读亦从旧。辅氏外甥之说。未知何据。然此等处。既非义理大头脑。则只当两存其说。以备参考。今欲强为辨论。则恐有穿凿之失。
御制条问曰。诗言婚姻之礼多矣。而皆称美其德也。鹊巢诗曰。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美其专静纯一也。何彼秾矣诗曰。曷不肃雍。王姬之车。美其敬而且和也。东山诗曰。之子于归。皇驳其马。美其新之孔嘉也。皆取其德。非徒称车马之盛也。今韩奕诗曰。韩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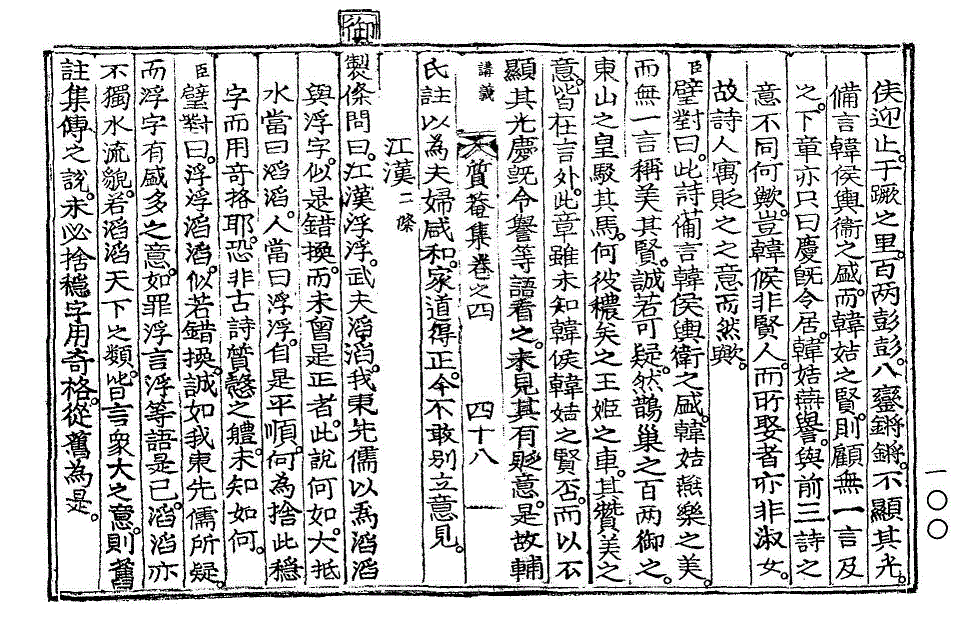 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銮锵锵。不显其光。备言韩侯舆卫之盛。而韩姞之贤。则顾无一言及之。下章亦只曰庆既令居。韩姞燕誉。与前三诗之意不同何欤。岂韩侯非贤人。而所娶者亦非淑女。故诗人寓贬之之意而然欤。
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銮锵锵。不显其光。备言韩侯舆卫之盛。而韩姞之贤。则顾无一言及之。下章亦只曰庆既令居。韩姞燕誉。与前三诗之意不同何欤。岂韩侯非贤人。而所娶者亦非淑女。故诗人寓贬之之意而然欤。臣璧对曰。此诗备言韩侯舆卫之盛。韩姞燕乐之美。而无一言称美其贤。诚若可疑。然鹊巢之百两御之。东山之皇驳其马。何彼秾矣之王姬之车。其赞美之意。皆在言外。此章虽未知韩侯韩姞之贤否。而以不显其光庆既令誉等语看之。未见其有贬意。是故辅氏注以为夫妇咸和。家道得正。今不敢别立意见。
江汉(二条)
御制条问曰。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我东先儒以为滔滔与浮字。似是错换。而未曾是正者。此说何如。大抵水当曰滔滔。人当曰浮浮。自是平顺。何为舍此稳字而用奇格耶。恐非古诗质悫之体。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浮浮滔滔。似若错换。诚如我东先儒所疑。而浮字有盛多之意。如罪浮言浮等语是已。滔滔亦不独水流貌。若滔滔天下之类。皆言众大之意。则旧注集传之说。未必舍稳字用奇格。从旧为是。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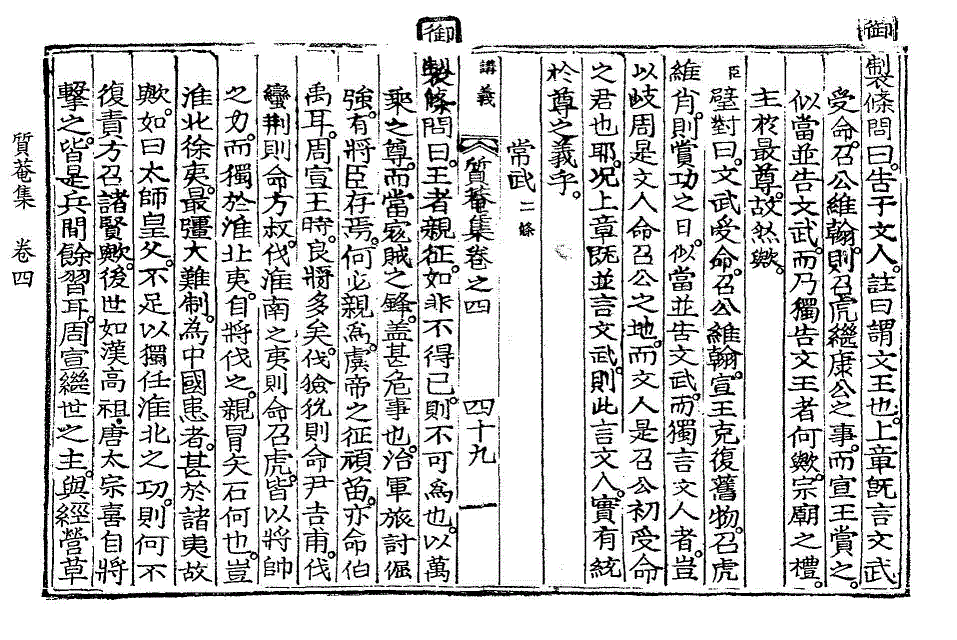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告于文人。注曰谓文王也。上章既言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则召虎继康公之事。而宣王赏之。似当并告文武。而乃独告文王者何欤。宗庙之礼。主于最尊。故然欤。
御制条问曰。告于文人。注曰谓文王也。上章既言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则召虎继康公之事。而宣王赏之。似当并告文武。而乃独告文王者何欤。宗庙之礼。主于最尊。故然欤。臣璧对曰。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宣王克复旧物。召虎维肖。则赏功之日。似当并告文武。而独言文人者。岂以岐周是文人命召公之地。而文人是召公初受命之君也耶。况上章既并言文武。则此言文人。实有统于尊之义乎。
常武(二条)
御制条问曰。王者亲征。如非不得已。则不可为也。以万乘之尊。而当寇贼之锋。盖甚危事也。治军旅讨倔强。有将臣存焉。何必亲为。虞帝之征顽苗。亦命伯禹耳。周宣王时。良将多矣。伐猃狁则命尹吉甫。伐蛮荆则命方叔。伐淮南之夷则命召虎。皆以将帅之力。而独于淮北夷。自将伐之。亲冒矢石何也。岂淮北徐夷。最彊大难制。为中国患者。甚于诸夷故欤。如曰太师皇父。不足以独任淮北之功。则何不复责方召诸贤欤。后世如汉高祖,唐太宗喜自将击之。皆是兵间馀习耳。周宣继世之主。与经营草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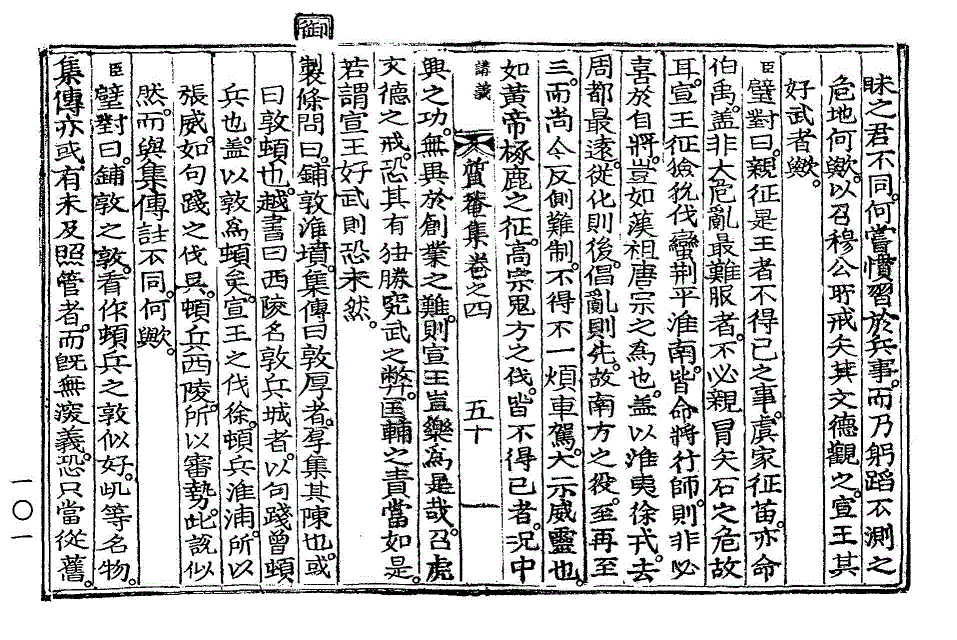 眛之君不同。何尝惯习于兵事。而乃躬蹈不测之危地何欤。以召穆公所戒矢其文德观之。宣王其好武者欤。
眛之君不同。何尝惯习于兵事。而乃躬蹈不测之危地何欤。以召穆公所戒矢其文德观之。宣王其好武者欤。臣璧对曰。亲征是王者不得已之事。虞家征苗。亦命伯禹。盖非大危乱最难服者。不必亲冒矢石之危故耳。宣王征猃狁伐蛮荆平淮南。皆命将行师。则非必喜于自将。岂如汉祖唐宗之为也。盖以淮夷徐戎。去周都最远。从化则后。倡乱则先。故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而尚今反侧难制。不得不一烦车驾。大示威灵也。如黄帝椓鹿之征。高宗鬼方之伐。皆不得已者。况中兴之功。无异于创业之难。则宣王岂乐为是哉。召虎文德之戒。恐其有狃胜究武之弊。匡辅之责当如是。若谓宣王好武则恐未然。
御制条问曰。铺敦淮坟。集传曰敦厚者。厚集其陈也。或曰敦顿也。越书曰西陵名敦兵城者。以句践曾顿兵也。盖以敦为顿矣。宣王之伐徐。顿兵淮浦。所以张威。如句践之伐吴。顿兵西陵。所以审势。此说似然。而与集传注不同。何欤。
臣璧对曰。铺敦之敦。看作顿兵之敦似好。此等名物。集传亦或有未及照管者。而既无深义。恐只当从旧。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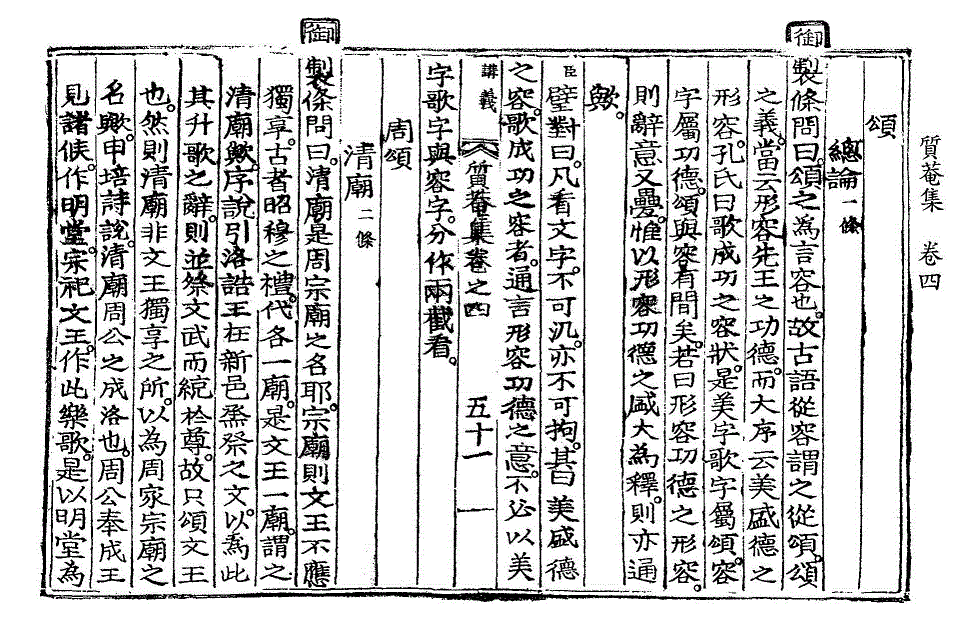 颂
颂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颂之为言容也。故古语从容谓之从颂。颂之义。当云形容先王之功德。而大序云美盛德之形容。孔氏曰歌成功之容状。是美字歌字属颂。容字属功德。颂与容有间矣。若曰形容功德之形容。则辞意又叠。惟以形容功德之盛大为释。则亦通欤。
臣璧对曰。凡看文字。不可汎。亦不可拘。其曰美盛德之容。歌成功之容者。通言形容功德之意。不必以美字歌字与容字。分作两截看。
周颂
清庙(二条)
御制条问曰。清庙是周宗庙之名耶。宗庙则文王不应独享。古者昭穆之礼。代各一庙。是文王一庙。谓之清庙欤。序说引洛诰王在新邑烝祭之文。以为此其升歌之辞。则并祭文武而统于尊。故只颂文王也。然则清庙非文王独享之所。以为周家宗庙之名欤。申培诗说。清庙周公之成洛也。周公奉成王见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作此乐歌。是以明堂为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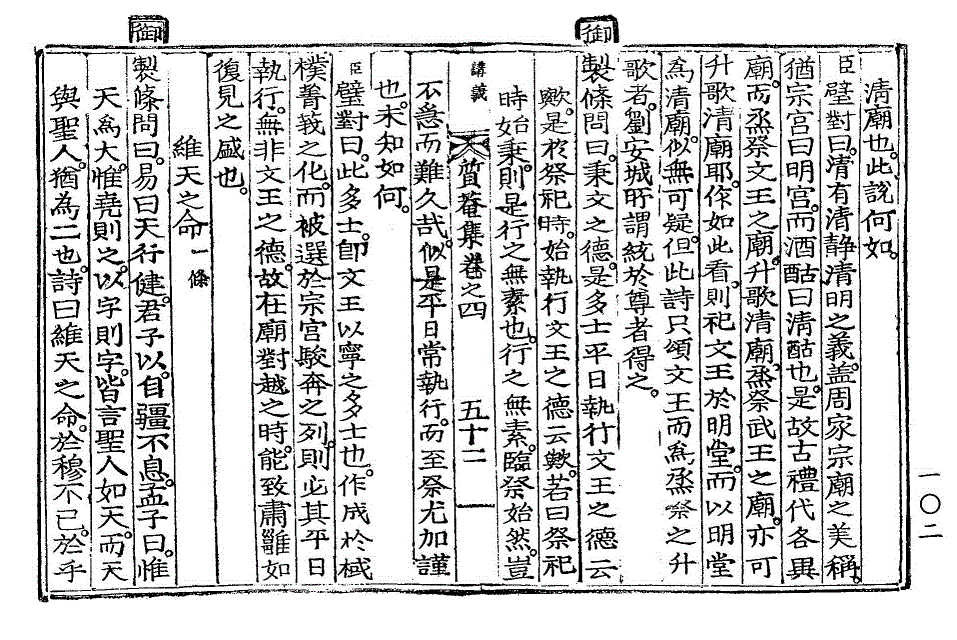 清庙也。此说何如。
清庙也。此说何如。臣璧对曰。清有清静清明之义。盖周家宗庙之美称。犹宗宫曰明宫。而酒酤曰清酤也。是故古礼代各异庙。而烝祭文王之庙。升歌清庙。烝祭武王之庙。亦可升歌清庙耶。作如此看。则祀文王于明堂。而以明堂为清庙。似无可疑。但此诗只颂文王而为烝祭之升歌者。刘安城所谓统于尊者得之。
御制条问曰。秉文之德。是多士平日执行文王之德云欤。是于祭祀时。始执行文王之德云欤。若曰祭祀时始秉。则是行之无素也。行之无素。临祭始然。岂不急而难久哉。似是平日常执行。而至祭尤加谨也。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多士。即文王以宁之多士也。作成于棫朴菁莪之化。而被选于宗宫骏奔之列。则必其平日执行。无非文王之德。故在庙对越之时。能致肃雍如复见之盛也。
维天之命(一条)
御制条问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孟子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以字则字。皆言圣人如天。而天与圣人。犹为二也。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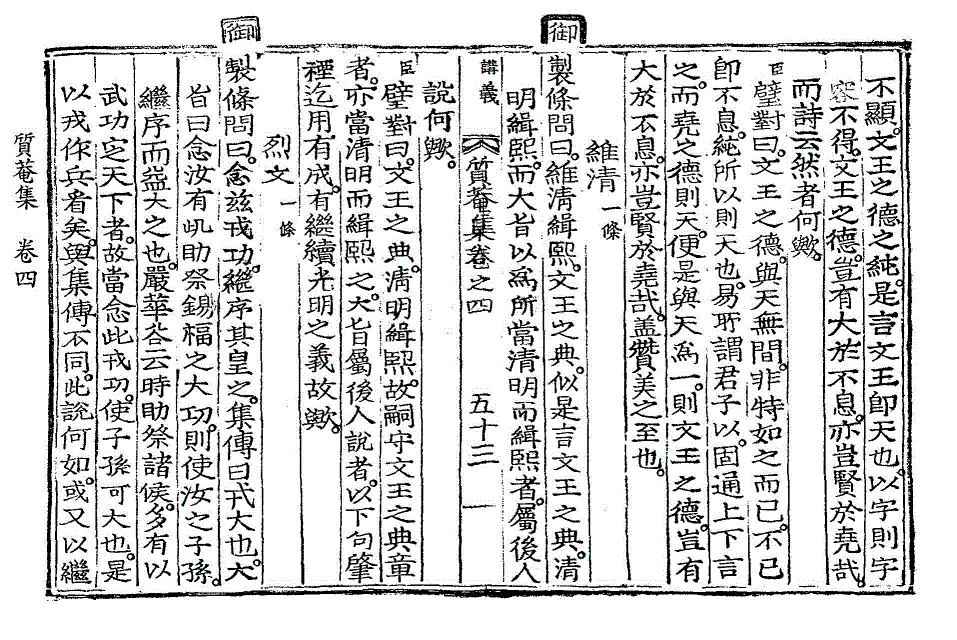 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是言文王即天也。以字则字容不得。文王之德。岂有大于不息。亦岂贤于尧哉。而诗云然者何欤。
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是言文王即天也。以字则字容不得。文王之德。岂有大于不息。亦岂贤于尧哉。而诗云然者何欤。臣璧对曰。文王之德。与天无间。非特如之而已。不已即不息。纯所以则天也。易所谓君子以。固通上下言之。而尧之德则天。便是与天为一。则文王之德。岂有大于不息。亦岂贤于尧哉。盖赞美之至也。
维清(一条)
御制条问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似是言文王之典。清明缉熙。而大旨以为所当清明而缉熙者。属后人说何欤。
臣璧对曰。文王之典。清明缉熙。故嗣守文王之典章者。亦当清明而缉熙之。大旨属后人说者。以下句肇禋迄用有成。有继续光明之义故欤。
烈文(一条)
御制条问曰。念玆戎功。继序其皇之。集传曰戎大也。大旨曰念汝有此助祭锡福之大功。则使汝之子孙。继序而益大之也。严华谷云时助祭诸侯。多有以武功定天下者。故当念此戎功。使子孙可大也。是以戎作兵看矣。与集传不同。此说何如。或又以继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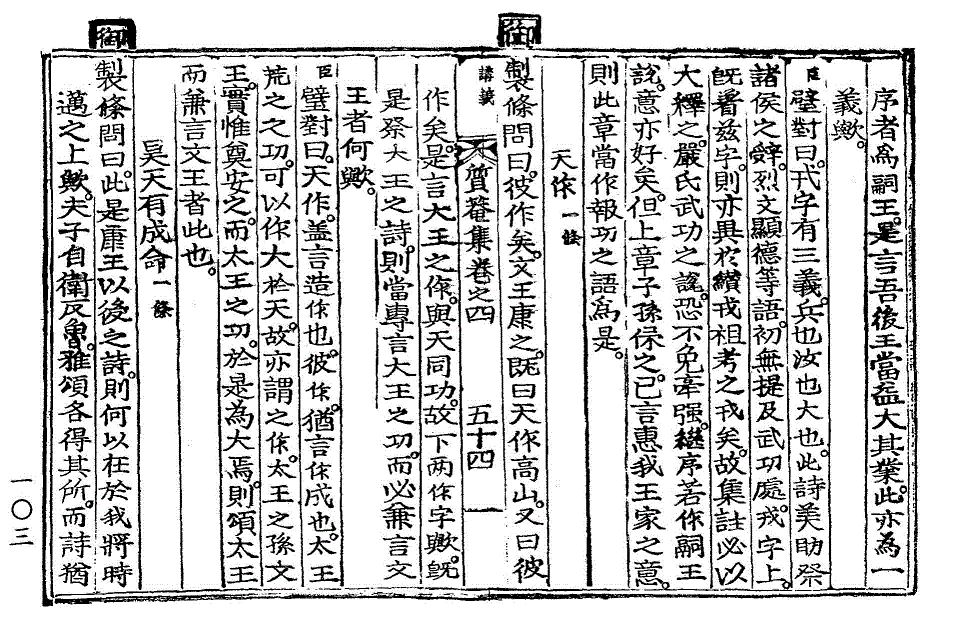 序者为嗣王。是言吾后王当益大其业。此亦为一义欤。
序者为嗣王。是言吾后王当益大其业。此亦为一义欤。臣璧对曰。戎字有三义。兵也汝也大也。此诗美助祭诸侯之辞。烈文显德等语。初无提及武功处。戎字上。既着玆字。则亦异于缵戎祖考之戎矣。故集注必以大释之。严氏武功之说。恐不免牵强。继序若作嗣王说。意亦好矣。但上章子孙保之。已言惠我王家之意。则此章当作报功之语为是。
天作(一条)
御制条问曰。彼作矣。文王康之。既曰天作高山。又曰彼作矣。是言大王之作。与天同功。故下两作字欤。既是祭大王之诗。则当专言大王之功。而必兼言文王者何欤。
臣璧对曰。天作。盖言造作也。彼作。犹言作成也。太王荒之之功。可以作大于天。故亦谓之作。太王之孙文王。实惟奠安之。而太王之功。于是为大焉。则颂太王而兼言文王者此也。
昊天有成命(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是康王以后之诗。则何以在于我将时迈之上欤。夫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而诗犹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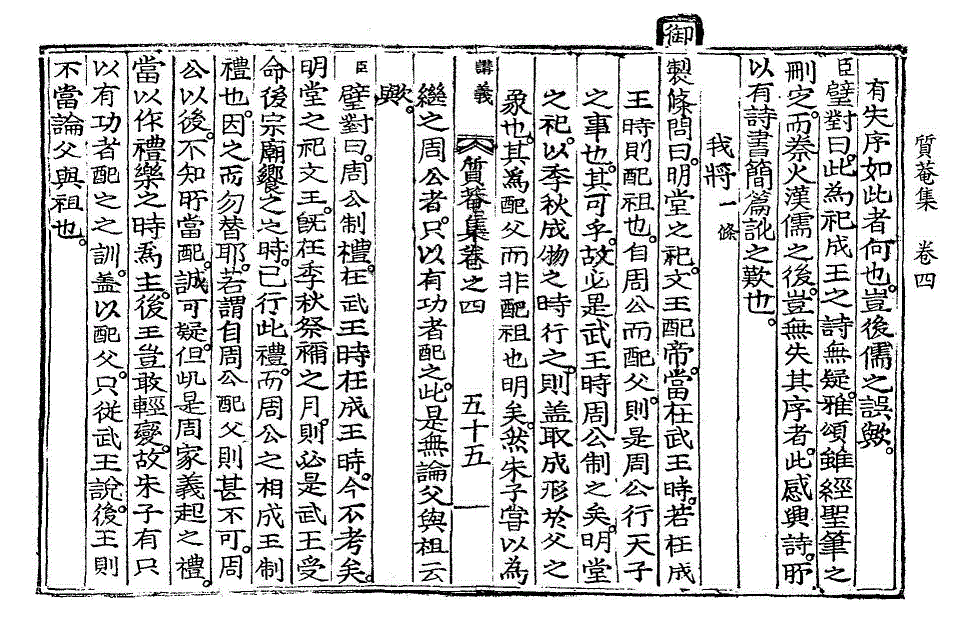 有失序如此者何也。岂后儒之误欤。
有失序如此者何也。岂后儒之误欤。臣璧对曰。此为祀成王之诗无疑。雅颂虽经圣笔之删定。而秦火汉儒之后。岂无失其序者。此感兴诗。所以有诗书简篇讹之叹也。
我将(一条)
御制条问曰。明堂之祀。文王配帝。当在武王时。若在成王时则配祖也。自周公而配父。则是周公行天子之事也。其可乎。故必是武王时周公制之矣。明堂之祀。以季秋成物之时行之。则盖取成形于父之象也。其为配父而非配祖也明矣。然朱子尝以为继之周公者。只以有功者配之。此是无论父与祖云欤。
臣璧对曰。周公制礼。在武王时在成王时。今不考矣。明堂之祀文王。既在季秋祭祢之月。则必是武王受命后宗庙飨之之时。已行此礼。而周公之相成王制礼也。因之而勿替耶。若谓自周公配父则甚不可。周公以后。不知所当配。诚可疑。但此是周家义起之礼。当以作礼乐之时为主。后王岂敢轻变。故朱子有只以有功者配之之训。盖以配父。只从武王说。后王则不当论父与祖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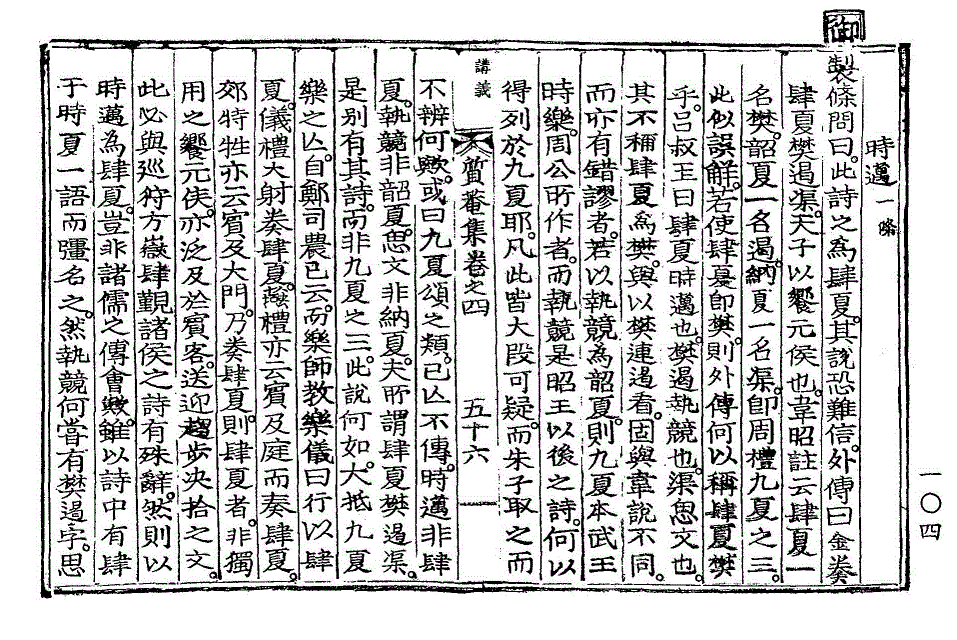 时迈(一条)
时迈(一条)御制条问曰。此诗之为肆夏。其说恐难信。外传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飨元侯也。韦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即周礼九夏之三。此似误解。若使肆夏即樊。则外传何以称肆夏樊乎。吕叔玉曰肆夏时迈也。樊遏执竞也。渠思文也。其不称肆夏为樊。与以樊连遏看。固与韦说不同。而亦有错谬者。若以执竞为韶夏。则九夏本武王时乐。周公所作者。而执竞是昭王以后之诗。何以得列于九夏耶。凡此皆大段可疑。而朱子取之而不辨何欤。或曰九夏颂之类。已亡不传。时迈非肆夏。执竞非韶夏。思文非纳夏。夫所谓肆夏樊遏渠。是别有其诗。而非九夏之三。此说何如。大抵九夏乐之亡。自郑司农已云。而乐师教乐仪曰行以肆夏。仪礼大射奏肆夏。燕礼亦云宾及庭而奏肆夏。郊特牲亦云宾及大门。乃奏肆夏。则肆夏者。非独用之飨元侯。亦泛及于宾客。送迎趋步决拾之文。此必与巡狩方岳肆觐诸侯之诗有殊辞。然则以时迈为肆夏。岂非诸儒之傅会欤。虽以诗中有肆于时夏一语而彊名之。然执竞何尝有樊遏字。思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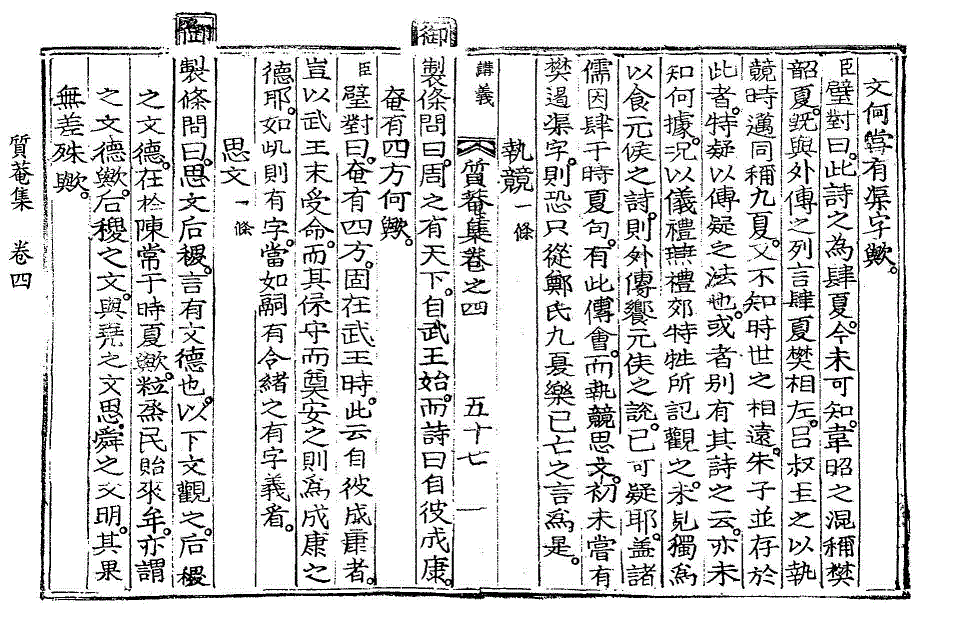 文何尝有渠字欤。
文何尝有渠字欤。臣璧对曰。此诗之为肆夏。今未可知。韦昭之混称樊韶夏。既与外传之列言肆夏樊相左。吕叔玉之以执竞时迈同称九夏。又不知时世之相远。朱子并存于此者。特疑以传疑之法也。或者别有其诗之云。亦未知何据。况以仪礼燕礼郊特牲所记观之。未见独为以食元侯之诗。则外传飨元侯之说。已可疑耶。盖诸儒因肆于时夏句。有此傅会。而执竞思文。初未尝有樊遏渠字。则恐只从郑氏九夏乐已亡之言为是。
执竞(一条)
御制条问曰。周之有天下。自武王始。而诗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何欤。
臣璧对曰。奄有四方。固在武王时。此云自彼成康者。岂以武王末受命。而其保守而奠安之则为成康之德耶。如此则有字。当如嗣有令绪之有字义看。
思文(一条)
御制条问曰。思文后稷。言有文德也。以下文观之。后稷之文德。在于陈常于时夏欤。粒烝民贻来牟。亦谓之文德欤。后稷之文。与尧之文思,舜之文明。其果无差殊欤。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5L 页
 臣璧对曰。圣人之德。舍刑威征讨之外。皆文也。陈常时夏。固后稷之文德。而粒民之极。贻牟之惠。夫孰非后稷之文德乎。尧之文思。舜之文明。皆盛德之著于外者。而后稷之文。亦圣人之文。恐不可差殊看。
臣璧对曰。圣人之德。舍刑威征讨之外。皆文也。陈常时夏。固后稷之文德。而粒民之极。贻牟之惠。夫孰非后稷之文德乎。尧之文思。舜之文明。皆盛德之著于外者。而后稷之文。亦圣人之文。恐不可差殊看。臣工之什
臣工(一条)
御制条问曰。王釐尔成。来咨来茹。盖总言群臣百工。各以其职。当来咨度成宪。而农官尤当然也。小注辅庆源以为稼穑之事。群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来咨度农事之成法。恐非是。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此诗重在农事上。告群臣百工以来咨来度者。盖周家务本之政也。下章钱镈铚艾等事。即其所咨所度者。辅氏说恐得之。若以为总言各以其职。咨度成宪。则语意虽圆。而下章但言农事。无乃失于偏乎。
振鹭(一条)
御制条问曰。庶几夙夜。以永终誉。是赞美之辞。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最难保者令誉。故亦以此勉戒之欤。
臣璧对曰。永终二字。可见爱人以德之意。善始易。善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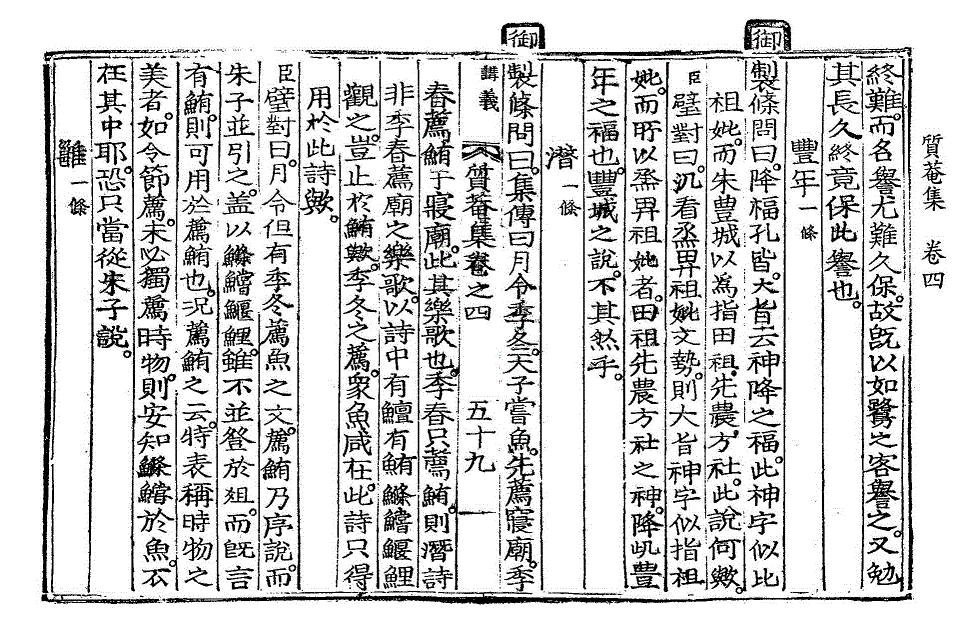 终难。而名誉尤难久保。故既以如鹭之客誉之。又勉其长久终竟保此誉也。
终难。而名誉尤难久保。故既以如鹭之客誉之。又勉其长久终竟保此誉也。丰年(一条)
御制条问曰。降福孔皆。大旨云神降之福。此神字似比祖妣。而朱礼城以为指田祖,先农,方社。此说何欤。
臣璧对曰。汎看烝畀祖妣文势。则大旨神字似指祖妣。而所以烝畀祖妣者。田祖先农方社之神。降此礼年之福也。丰城之说。不其然乎。
潜(一条)
御制条问曰。集传曰月令季冬。天子尝鱼。先荐寝庙。季春荐鲔于寝庙。此其乐歌也。季春只荐鲔。则潜诗非季春荐庙之乐歌。以诗中有鳣有鲔鲦鲿鰋鲤观之。岂止于鲔欤。季冬之荐。众鱼咸在。此诗只得用于此诗欤。
臣璧对曰。月令但有季冬荐鱼之文。荐鲔乃序说。而朱子并引之。盖以鲦鲿鰋鲤。虽不并登于俎。而既言有鲔。则可用于荐鲔也。况荐鲔之云。特表称时物之美者。如令节荐。未必独荐时物。则安知鲦𩼝于鱼。不在其中耶。恐只当从朱子说。
雍(一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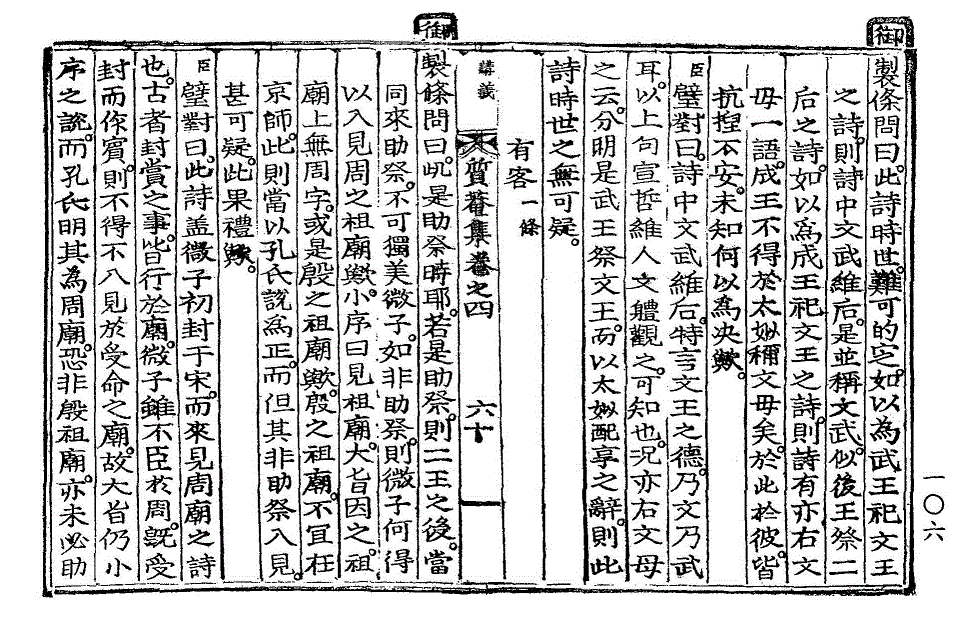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此诗时世。难可的定。如以为武王祀文王之诗。则诗中文武维后。是并称文武。似后王祭二后之诗。如以为成王祀文王之诗。则诗有亦右文母一语。成王不得于太姒称文母矣。于此于彼。皆抗捏不安。未知何以为决欤。
御制条问曰。此诗时世。难可的定。如以为武王祀文王之诗。则诗中文武维后。是并称文武。似后王祭二后之诗。如以为成王祀文王之诗。则诗有亦右文母一语。成王不得于太姒称文母矣。于此于彼。皆抗捏不安。未知何以为决欤。臣璧对曰。诗中文武维后。特言文王之德。乃文乃武耳。以上句宣哲维人文体观之。可知也。况亦右文母之云。分明是武王祭文王。而以太姒配享之辞。则此诗时世之无可疑。
有客(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是助祭时耶。若是助祭。则二王之后。当同来助祭。不可独美微子。如非助祭。则微子何得以入见周之祖庙欤。小序曰见祖庙。大旨因之。祖庙上无周字。或是殷之祖庙欤。殷之祖庙。不宜在京师。此则当以孔氏说为正。而但其非助祭入见。甚可疑。此果礼欤。
臣璧对曰。此诗盖微子初封于宋。而来见周庙之诗也。古者封赏之事。皆行于庙。微子虽不臣于周。既受封而作宾。则不得不入见于受命之庙。故大旨仍小序之说。而孔氏明其为周庙。恐非殷祖庙。亦未必助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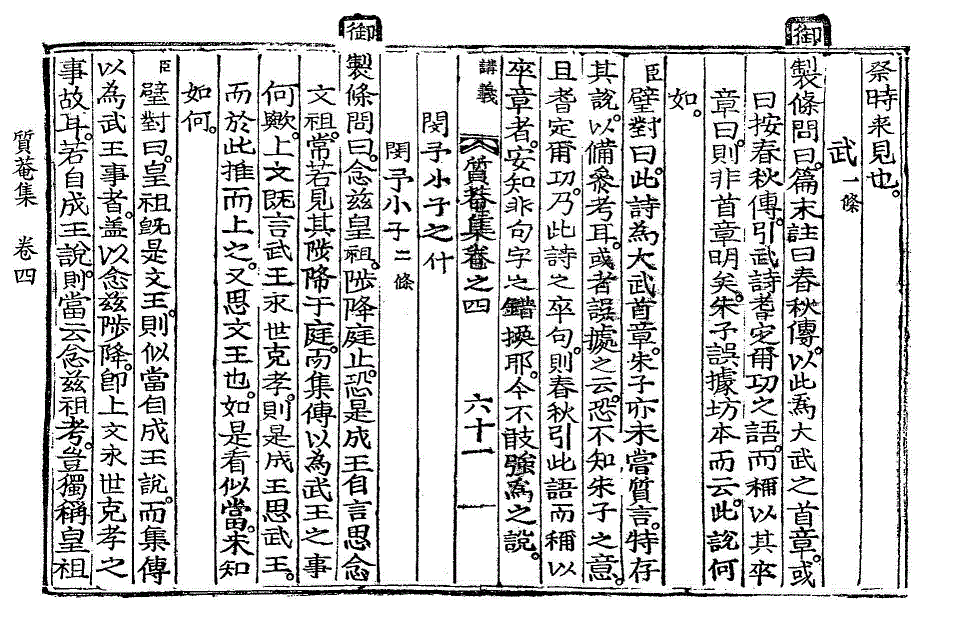 祭时来见也。
祭时来见也。武(一条)
御制条问曰。篇末注曰春秋传。以此为大武之首章。或曰按春秋传。引武诗耆定尔功之语。而称以其卒章曰。则非首章明矣。朱子误据坊本而云。此说何如。
臣璧对曰。此诗为大武首章。朱子亦未尝质言。特存其说。以备参考耳。或者误据之云。恐不知朱子之意。且耆定尔功。乃此诗之卒句。则春秋引此语而称以卒章者。安知非句字之错换耶。今不敢强为之说。
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二条)
御制条问曰。念玆皇祖。陟降庭止。恐是成王自言思念文祖。常若见其陟降于庭。而集传以为武王之事何欤。上文既言武王永世克孝。则是成王思武王。而于此推而上之。又思文王也。如是看似当。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皇祖既是文王。则似当自成王说。而集传以为武王事者。盖以念玆陟降。即上文永世克孝之事故耳。若自成王说。则当云念玆祖考。岂独称皇祖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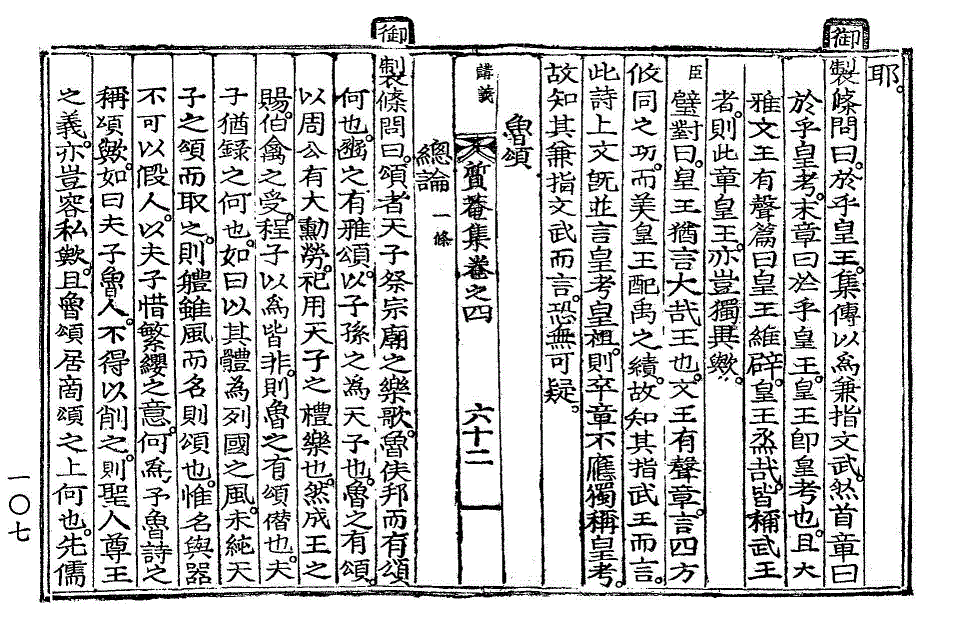 耶。
耶。御制条问曰。于乎皇王。集传以为兼指文武。然首章曰于乎皇考。末章曰于乎皇王。皇王即皇考也。且大雅文王有声篇曰皇王维辟。皇王烝哉。皆称武王者。则此章皇王。亦岂独异欤。
臣璧对曰。皇王犹言大哉王也。文王有声章。言四方攸同之功。而美皇王配禹之绩。故知其指武王而言。此诗上文既并言皇考皇祖。则卒章不应独称皇考。故知其兼指文武而言。恐无可疑。
鲁颂
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颂者天子祭宗庙之乐歌。鲁侯邦而有颂何也。豳之有雅颂。以子孙之为天子也。鲁之有颂。以周公有大勋劳。祀用天子之礼乐也。然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程子以为皆非。则鲁之有颂僭也。夫子犹录之何也。如曰以其体为列国之风。未纯天子之颂而取之。则体虽风而名则颂也。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以夫子惜繁缨之意。何为予鲁诗之称颂欤。如曰夫子鲁人。不得以削之。则圣人尊王之义。亦岂容私欤。且鲁颂居商颂之上何也。先儒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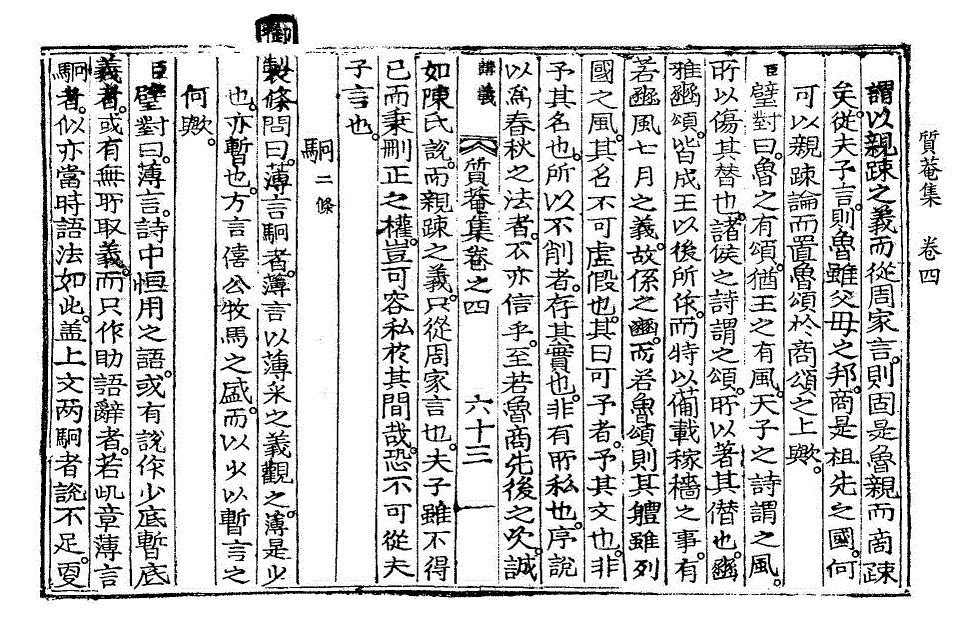 谓以亲疏之义而从周家言。则固是鲁亲而商疏矣。从夫子言。则鲁虽父母之邦。商是祖先之国。何可以亲疏论而置鲁颂于商颂之上欤。
谓以亲疏之义而从周家言。则固是鲁亲而商疏矣。从夫子言。则鲁虽父母之邦。商是祖先之国。何可以亲疏论而置鲁颂于商颂之上欤。臣璧对曰。鲁之有颂。犹王之有风。天子之诗谓之风。所以伤其替也。诸侯之诗谓之颂。所以著其僭也。豳雅豳颂。皆成王以后所作。而特以备载稼穑之事。有若豳风七月之义。故系之豳。而若鲁颂则其体虽列国之风。其名不可虚假也。其曰可予者。予其文也。非予其名也。所以不削者。存其实也。非有所私也。序说以为春秋之法者。不亦信乎。至若鲁商先后之次。诚如陈氏说。而亲疏之义。只从周家言也。夫子虽不得已而秉删正之权。岂可容私于其间哉。恐不可从夫子言也。
駉(二条)
御制条问曰。薄言駉者。薄言以薄采之义观之。薄是少也。亦暂也。方言僖公牧马之盛。而以少以暂言之何欤。
臣璧对曰。薄言。诗中恒用之语。或有说作少底暂底义者。或有无所取义。而只作助语辞者。若此章薄言駉者。似亦当时语法如此。盖上文两駉者说不足。更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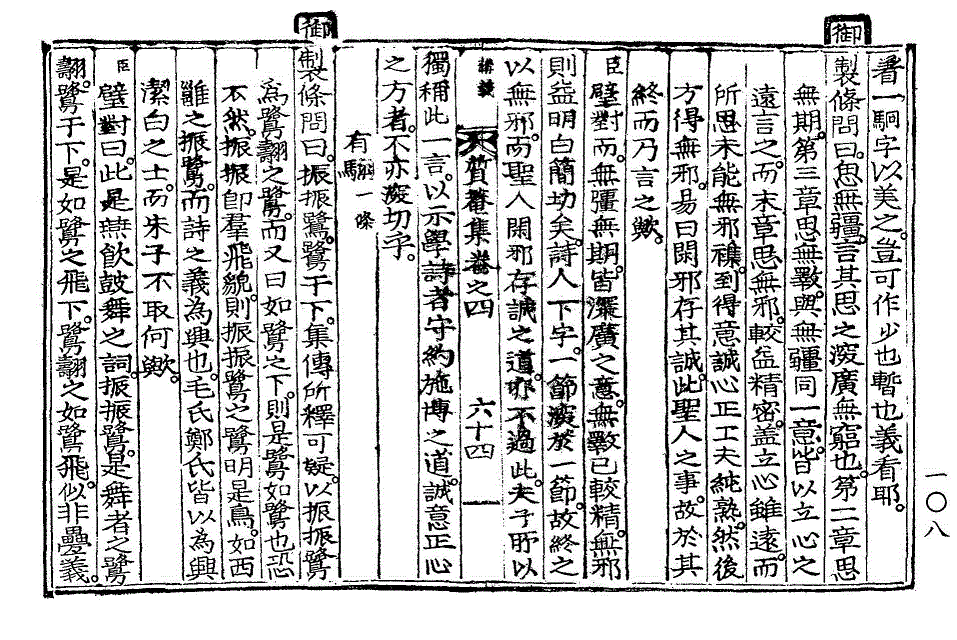 着一駉字以美之。岂可作少也暂也义看耶。
着一駉字以美之。岂可作少也暂也义看耶。御制条问曰。思无疆。言其思之深广无穷也。第二章思无期。第三章思无斁。与无疆同一意。皆以立心之远言之。而末章思无邪。较益精密。盖立心虽远。而所思未能无邪杂。到得意诚心正工夫纯熟。然后方得无邪。易曰闲邪存其诚。此圣人之事。故于其终而乃言之欤。
臣璧对而。无彊无期。皆深广之意。无斁已较精。无邪则益明白简切矣。诗人下字。一节深于一节。故终之以无邪。而圣人闲邪存诚之道。亦不过此。夫子所以独称此一言。以示学诗者守约施博之道。诚意正心之方者。不亦深切乎。
有駜(一条)
御制条问曰。振振鹭。鹭于下。集传所释可疑。以振振鹭为鹭翿之鹭。而又曰如鹭之下。则是鹭如鹭也恐不然。振振即群飞貌。则振振鹭之鹭明是鸟。如西雍之振鹭。而诗之义为兴也。毛氏郑氏皆以为兴洁白之士。而朱子不取何欤。
臣璧对曰。此是燕饮鼓舞之词。振振鹭。是舞者之鹭翿。鹭于下。是如鹭之飞下。鹭翿之如鹭飞。似非叠义。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9H 页
 如是看。文理为顺。若以振振鹭看作兴体。如西雍振鹭之鹭。则却是更多一鹭字。而上下文势不顺矣。集传不取毛郑之说。特以备一义者。恐无可疑。
如是看。文理为顺。若以振振鹭看作兴体。如西雍振鹭之鹭。则却是更多一鹭字。而上下文势不顺矣。集传不取毛郑之说。特以备一义者。恐无可疑。泮水(二条)
御制条问曰。申培诗说云僖公作泮宫而落其成。太史克商祷之。集传大旨只言饮于泮宫。而不言落成。非落成则其饮也。为何事而饮欤。古者泽宫。行大射之礼。射礼有饮。此为习射而饮欤。诗曰角弓其觓。束矢其搜。此言兵器之精利。可伐淮夷。未见其必为习射也。且以在泮献䤋之文。谓之告功饮至之辞。则考之前史。僖公无伐淮夷之事。此诗只是颂祝而愿其有是功。则亦不可谓以献捷而饮也。然则其饮也。必是为落成也。诗曰既作泮宫。岂非泮宫筑成之始欤。斯干之宫室既成而犹落之。况于泮宫乎。然而大旨不取落成之说何欤。
臣璧对曰。申培落成之说。既作泮宫一句外。无可考。而既作之云。非必创造也。鲁国旧来不应无学。虽曰僖公新修之。而前后在泮字。亦未见初作初至之义。若斯干诗全篇。皆言筑宫之事。则可知为落成之作。而此诗与斯干。殊不相似。且以献䤋献囚之文观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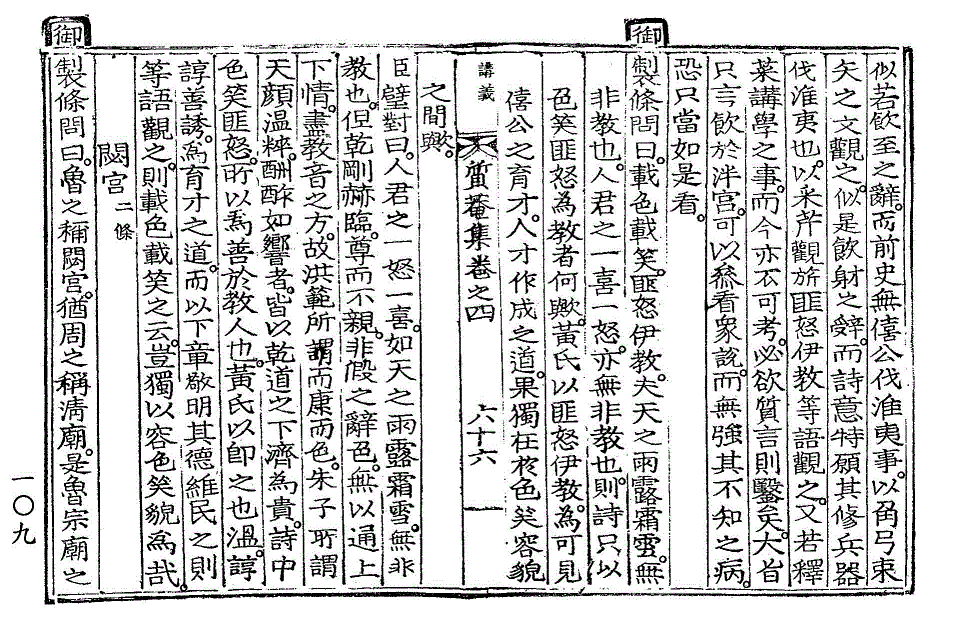 似若饮至之辞。而前史无僖公伐淮夷事。以角弓束矢之文观之。似是饮射之辞。而诗意特愿其修兵器伐淮夷也。以采芹观旂匪怒伊教等语观之。又若释菜讲学之事。而今亦不可考。必欲质言则凿矣。大旨只言饮于泮宫。可以参看众说。而无强其不知之病。恐只当如是看。
似若饮至之辞。而前史无僖公伐淮夷事。以角弓束矢之文观之。似是饮射之辞。而诗意特愿其修兵器伐淮夷也。以采芹观旂匪怒伊教等语观之。又若释菜讲学之事。而今亦不可考。必欲质言则凿矣。大旨只言饮于泮宫。可以参看众说。而无强其不知之病。恐只当如是看。御制条问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夫天之雨露霜雪。无非教也。人君之一喜一怒。亦无非教也。则诗只以色笑匪怒为教者何欤。黄氏以匪怒伊教。为可见僖公之育才。人才作成之道。果独在于色笑容貌之间欤。
臣璧对曰。人君之一怒一喜。如天之雨露霜雪。无非教也。但乾刚赫临。尊而不亲。非假之辞色。无以通上下情。尽教音之方。故洪范所谓而康而色。朱子所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者。皆以乾道之下济为贵。诗中色笑匪怒。所以为善于教人也。黄氏以即之也温。谆谆善诱。为育才之道。而以下章敬明其德维民之则等语观之。则载色载笑之云。岂独以容色笑貌为哉。
閟宫(二条)
御制条问曰。鲁之称閟宫。犹周之称清庙。是鲁宗庙之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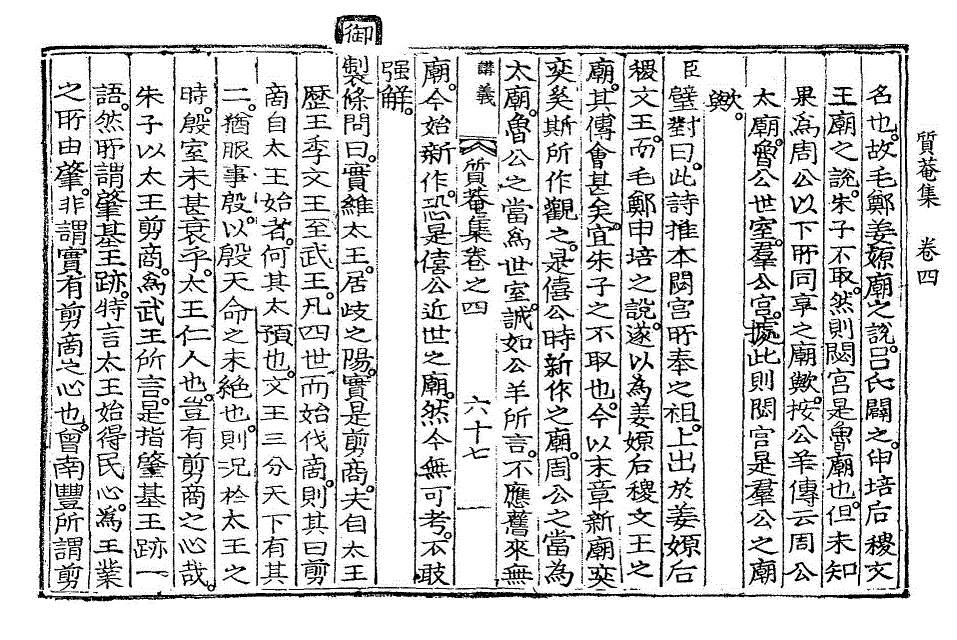 名也。故毛郑姜嫄庙之说。吕氏辟之。申培后稷文王庙之说。朱子不取。然则閟宫是鲁庙也。但未知果为周公以下所同享之庙欤。按公羊传云周公太庙。鲁公世室。群公宫。据此则閟宫是群公之庙欤。
名也。故毛郑姜嫄庙之说。吕氏辟之。申培后稷文王庙之说。朱子不取。然则閟宫是鲁庙也。但未知果为周公以下所同享之庙欤。按公羊传云周公太庙。鲁公世室。群公宫。据此则閟宫是群公之庙欤。臣璧对曰。此诗推本閟宫所奉之祖。上出于姜嫄后稷文王。而毛郑申培之说。遂以为姜嫄后稷文王之庙。其傅会甚矣。宜朱子之不取也。今以末章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观之。是僖公时新作之庙。周公之当为太庙。鲁公之当为世室。诚如公羊所言。不应旧来无庙。今始新作。恐是僖公近世之庙。然今无可考。不敢强解。
御制条问曰。实维太王。居歧之阳。实是剪商。夫自太王历王季文王至武王。凡四世而始伐商。则其曰剪商自太王始者。何其太预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以殷天命之未绝也。则况于太王之时。殷室未甚衰乎。太王仁人也。岂有剪商之心哉。朱子以太王剪商。为武王所言。是指肇基王迹一语。然所谓肇基王迹。特言太王始得民心。为王业之所由肇。非谓实有剪商之心也。曾南丰所谓剪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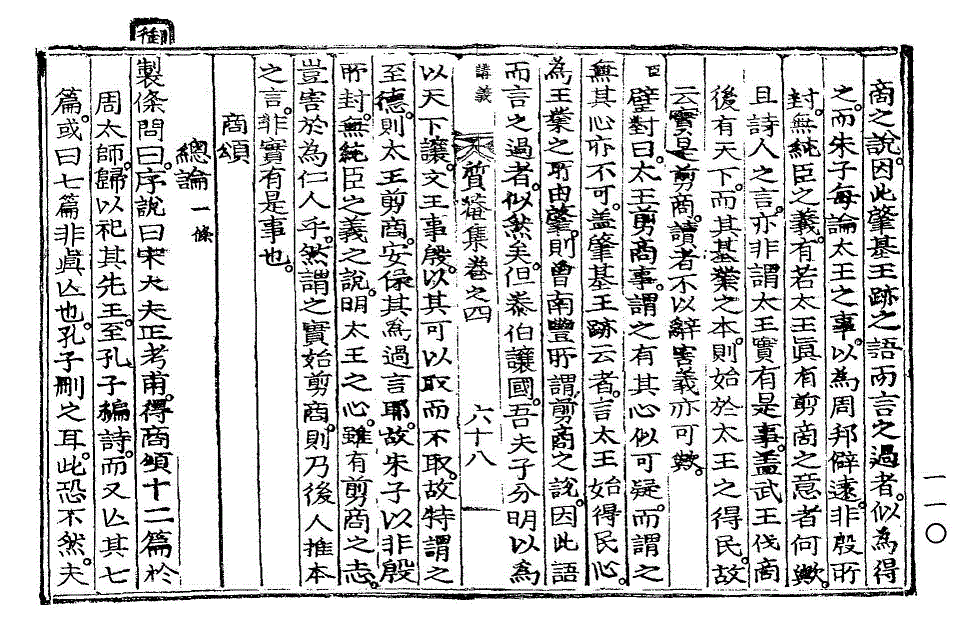 商之说。因此肇基王迹之语而言之过者。似为得之。而朱子每论太王之事。以为周邦僻远。非殷所封。无纯臣之义。有若太王真有剪商之意者何欤。且诗人之言。亦非谓太王实有是事。盖武王伐商后有天下。而其基业之本。则始于太王之得民。故云实是剪商。读者不以辞害义亦可欤。
商之说。因此肇基王迹之语而言之过者。似为得之。而朱子每论太王之事。以为周邦僻远。非殷所封。无纯臣之义。有若太王真有剪商之意者何欤。且诗人之言。亦非谓太王实有是事。盖武王伐商后有天下。而其基业之本。则始于太王之得民。故云实是剪商。读者不以辞害义亦可欤。臣璧对曰。太王剪商事。谓之有其心似可疑。而谓之无其心亦不可。盖肇基王迹云者。言太王始得民心。为王业之所由肇。则曾南丰所谓剪商之说。因此语而言之过者。似然矣。但泰伯让国。吾夫子分明以为以天下让。文王事殷。以其可以取而不取。故特谓之至德。则太王剪商。安保其为过言耶。故朱子以非殷所封。无纯臣之义之说。明太王之心。虽有剪商之志。岂害于为仁人乎。然谓之实始剪商。则乃后人推本之言。非实有是事也。
商颂
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序说曰宋大夫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而又亡其七篇。或曰七篇非真亡也。孔子删之耳。此恐不然。夫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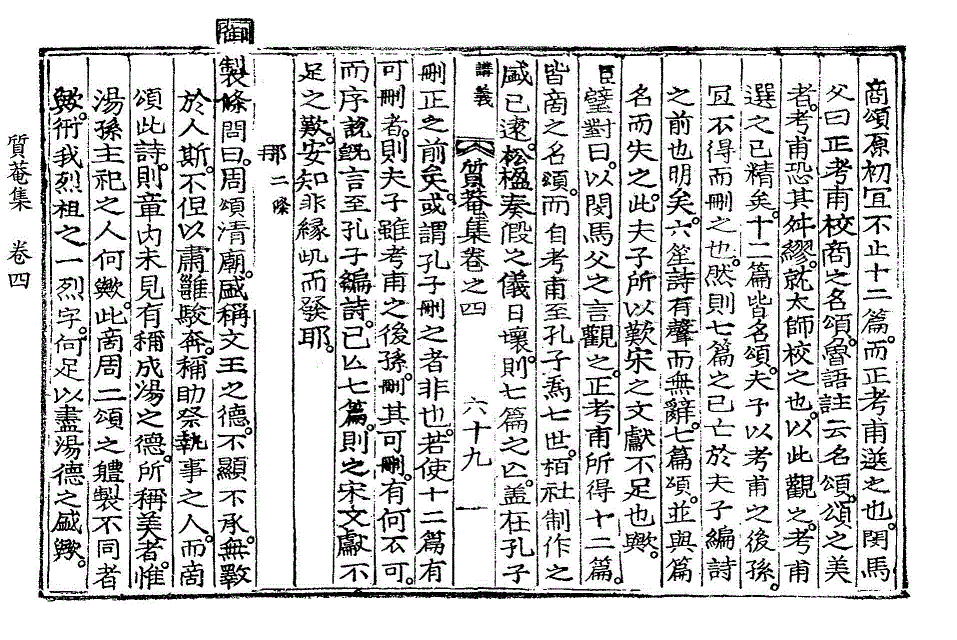 商颂原初宜不止十二篇。而正考甫选之也。闵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颂。鲁语注云名颂。颂之美者。考甫恐其舛缪。就太师校之也。以此观之。考甫选之已精矣。十二篇皆名颂。夫子以考甫之后孙。宜不得而删之也。然则七篇之已亡于夫子编诗之前也明矣。六笙诗有声而无辞。七篇颂。并与篇名而失之。此夫子所以叹宋之文献不足也欤。
商颂原初宜不止十二篇。而正考甫选之也。闵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颂。鲁语注云名颂。颂之美者。考甫恐其舛缪。就太师校之也。以此观之。考甫选之已精矣。十二篇皆名颂。夫子以考甫之后孙。宜不得而删之也。然则七篇之已亡于夫子编诗之前也明矣。六笙诗有声而无辞。七篇颂。并与篇名而失之。此夫子所以叹宋之文献不足也欤。臣璧对曰。以闵马父之言观之。正考甫所得十二篇。皆商之名颂。而自考甫至孔子为七世。柏社制作之盛已远。松楹奏假之仪日坏。则七篇之亡。盖在孔子删正之前矣。或谓孔子删之者非也。若使十二篇有可删者。则夫子虽考甫之后孙。删其可删。有何不可。而序说既言至孔子编诗。已亡七篇。则之宋文献不足之叹。安知非缘此而发耶。
那(二条)
御制条问曰。周颂清庙。盛称文王之德。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不但以肃雍骏奔。称助祭执事之人。而商颂此诗。则章内未见有称成汤之德。所称美者。惟汤孙主祀之人何欤。此商周二颂之体制不同者欤。衎我烈祖之一烈字。何足以尽汤德之盛欤。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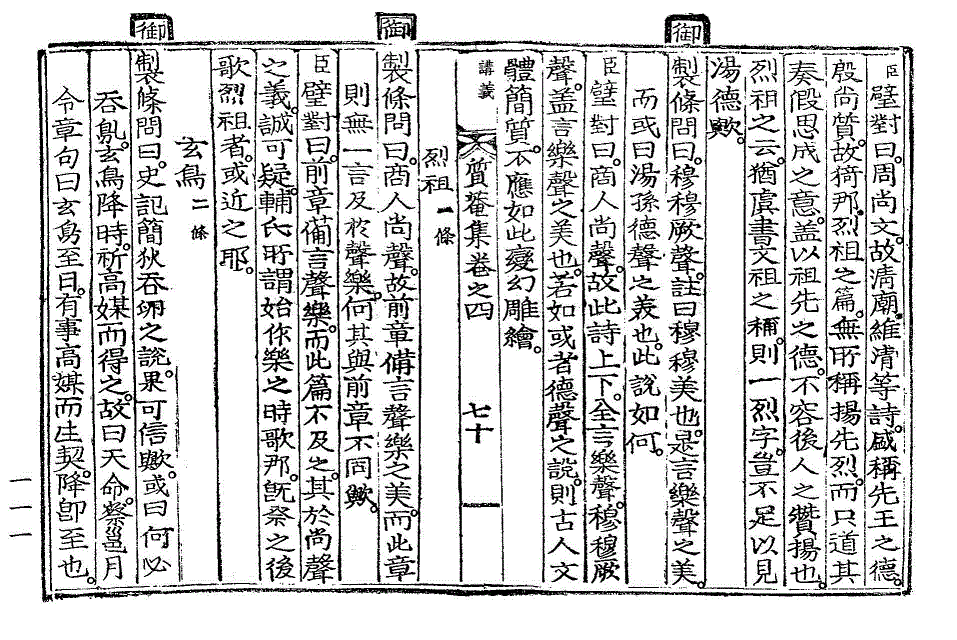 臣璧对曰。周尚文。故清庙,维清等诗。盛称先王之德。殷尚质。故猗那,烈祖之篇。无所称扬先烈。而只道其奏假思成之意。盖以祖先之德。不容后人之赞扬也。烈祖之云。犹虞书文祖之称。则一烈字。岂不足以见汤德欤。
臣璧对曰。周尚文。故清庙,维清等诗。盛称先王之德。殷尚质。故猗那,烈祖之篇。无所称扬先烈。而只道其奏假思成之意。盖以祖先之德。不容后人之赞扬也。烈祖之云。犹虞书文祖之称。则一烈字。岂不足以见汤德欤。御制条问曰。穆穆厥声。注曰穆穆美也。是言乐声之美。而或曰汤孙德声之美也。此说如何。
臣璧对曰。商人尚声。故此诗上下。全言乐声。穆穆厥声。盖言乐声之美也。若如或者德声之说。则古人文体简质。不应如此变幻雕绘。
烈祖(一条)
御制条问曰。商人尚声。故前章备言声乐之美。而此章则无一言及于声乐。何其与前章不同欤。
臣璧对曰。前章备言声乐。而此篇不及之。其于尚声之义。诚可疑。辅氏所谓始作乐之时歌那。既祭之后歌烈祖者。或近之耶。
玄鸟(二条)
御制条问曰。史记简狄吞卵之说。果可信欤。或曰何必吞鳦。玄鸟降时。祈高媒而得之。故曰天命。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鸟至日。有事高媒而生契。降即至也。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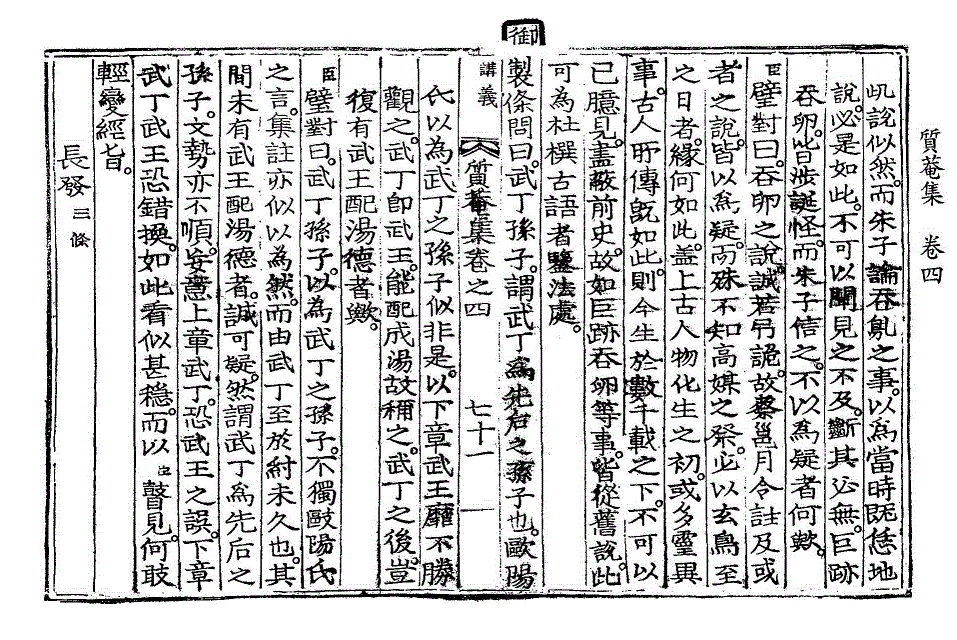 此说似然。而朱子论吞鳦之事。以为当时既恁地说。必是如此。不可以闻见之不及。断其必无。巨迹吞卵。皆涉诞怪。而朱子信之。不以为疑者何欤。
此说似然。而朱子论吞鳦之事。以为当时既恁地说。必是如此。不可以闻见之不及。断其必无。巨迹吞卵。皆涉诞怪。而朱子信之。不以为疑者何欤。臣璧对曰。吞卵之说。诚若吊诡。故蔡邕月令注及或者之说。皆以为疑。而殊不知高媒之祭。必以玄鸟至之日者。缘何如此。盖上古人物化生之初。或多灵异事。古人所传既如此。则今生于数千载之下。不可以己臆见。尽蔽前史。故如巨迹吞卵等事。皆从旧说。此可为杜㯢(一作撰)古语者鉴法处。
御制条问曰。武丁孙子。谓武丁为先后之孙子也。欧阳氏以为武丁之孙子似非是。以下章武王靡不胜观之。武丁即武王。能配成汤故称之。武丁之后。岂复有武王配汤德者欤。
臣璧对曰。武丁孙子。以为武丁之孙子。不独驱阳氏之言。集注亦似以为然。而由武丁至于纣未久也。其间未有武王配汤德者。诚可疑。然谓武丁为先后之孙子。文势亦不顺。妄意上章武丁。恐武王之误。下章武丁武王恐错换。如此看似甚稳。而以臣瞽见。何敢轻变经旨。
长发(三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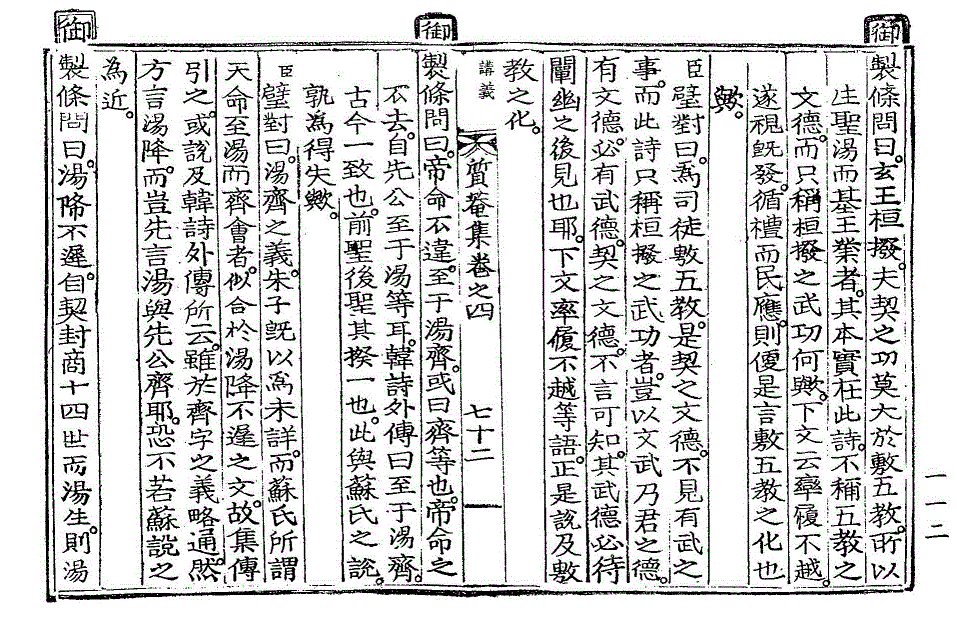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玄王桓拨。夫契之功莫大于敷五教。所以生圣汤而基王业者。其本实在此诗。不称五教之文德。而只称桓拨之武功何欤。下文云率履不越。遂视既发。循礼而民应。则便是言敷五教之化也欤。
御制条问曰。玄王桓拨。夫契之功莫大于敷五教。所以生圣汤而基王业者。其本实在此诗。不称五教之文德。而只称桓拨之武功何欤。下文云率履不越。遂视既发。循礼而民应。则便是言敷五教之化也欤。臣璧对曰。为司徒敷五教。是契之文德。不见有武之事。而此诗只称桓拨之武功者。岂以文武乃君之德。有文德。必有武德。契之文德。不言可知。其武德必待阐幽之后见也耶。下文率履不越等语。正是说及敷教之化。
御制条问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或曰齐等也。帝命之不去。自先公至于汤等耳。韩诗外传曰至于汤齐。古今一致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此与苏氏之说。孰为得失欤。
臣璧对曰。汤齐之义。朱子既以为未详。而苏氏所谓天命至汤而齐会者。似合于汤降不迟之文。故集传引之。或说及韩诗外传所云。虽于齐字之义略通。然方言汤降。而岂先言汤与先公齐耶。恐不若苏说之为近。
御制条问曰。汤降不迟。自契封商十四世而汤生。则汤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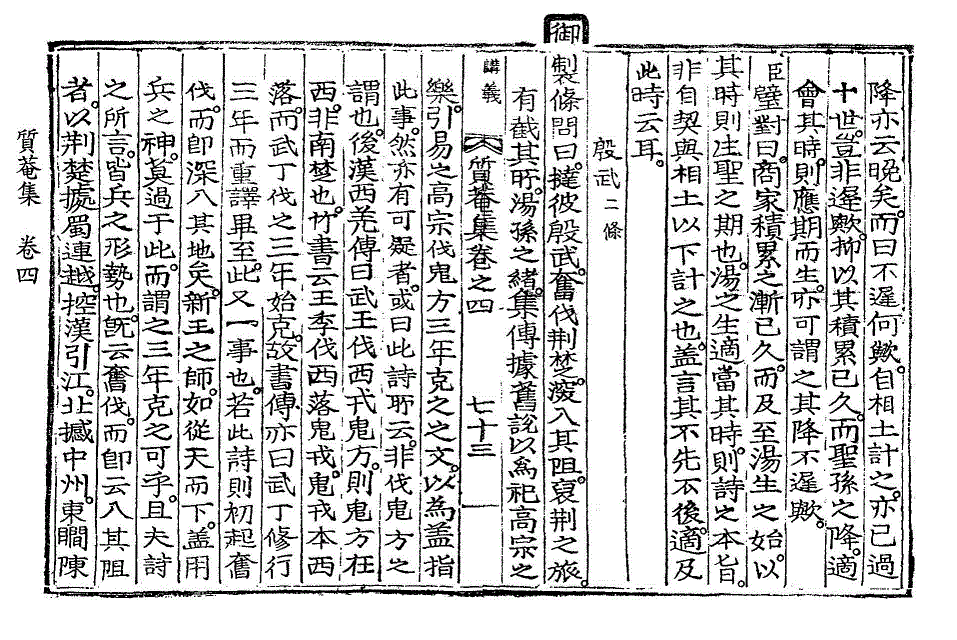 降亦云晚矣。而曰不迟何欤。自相土计之。亦已过十世。岂非迟欤。抑以其积累已久。而圣孙之降。适会其时。则应期而生。亦可谓之其降不迟欤。
降亦云晚矣。而曰不迟何欤。自相土计之。亦已过十世。岂非迟欤。抑以其积累已久。而圣孙之降。适会其时。则应期而生。亦可谓之其降不迟欤。臣璧对曰。商家积累之渐已久。而及至汤生之始。以其时则生圣之期也。汤之生适当其时。则诗之本旨。非自契与相土以下计之也。盖言其不先不后。适及此时云耳。
殷武(二条)
御制条问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集传据旧说以为祀高宗之乐。引易之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文。以为盖指此事。然亦有可疑者。或曰此诗所云。非伐鬼方之谓也。后汉西羌传曰武王伐西戎鬼方。则鬼方在西。非南楚也。竹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鬼戎本西落。而武丁伐之三年始克。故书传亦曰武丁修行三年而重译毕至。此又一事也。若此诗则初起奋伐。而即深入其地矣。新王之师。如从天而下。盖用兵之神。莫过于此。而谓之三年克之可乎。且夫诗之所言。皆兵之形势也。既云奋伐。而即云入其阻者。以荆楚据蜀连越。控汉引江。北撼中州。东瞷陈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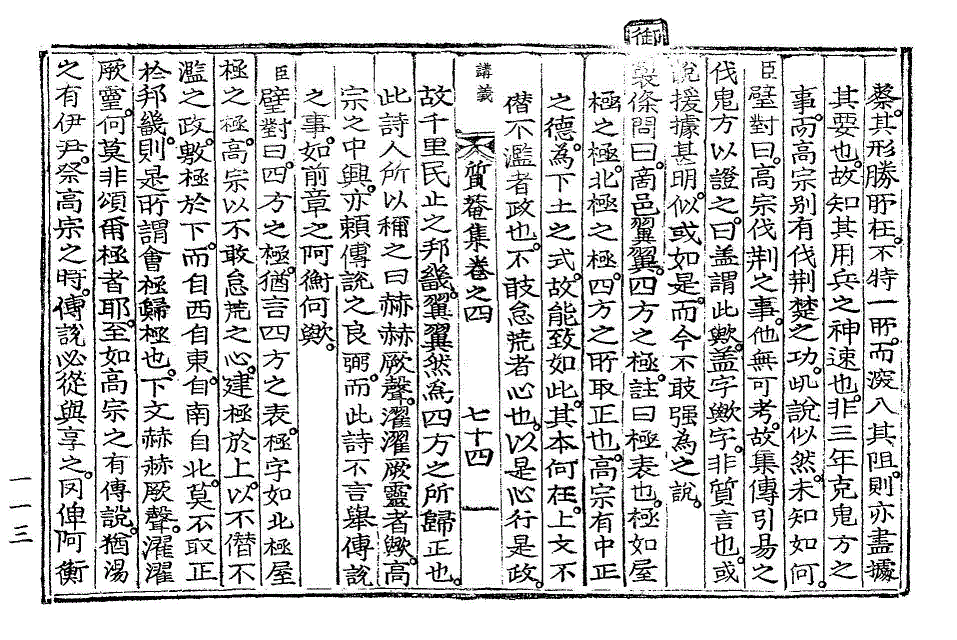 蔡。其形胜所在。不特一所。而深入其阻。则亦尽据其要也。故知其用兵之神速也。非三年克鬼方之事。而高宗别有伐荆楚之功。此说似然。未知如何。
蔡。其形胜所在。不特一所。而深入其阻。则亦尽据其要也。故知其用兵之神速也。非三年克鬼方之事。而高宗别有伐荆楚之功。此说似然。未知如何。臣璧对曰。高宗伐荆之事。他无可考。故集传引易之伐鬼方以證之。曰盖谓此欤。盖字欤字。非质言也。或说援据甚明。似或如是。而今不敢强为之说。
御制条问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注曰极表也。极如屋极之极。北极之极。四方之所取正也。高宗有中正之德。为下土之式。故能致如此。其本何在。上文不僭不滥者政也。不敢怠荒者心也。以是心行是政。故千里民止之邦畿。翼翼然为四方之所归正也。此诗人所以称之曰赫赫厥声。濯濯厥灵者欤。高宗之中兴。亦赖傅说之良弼。而此诗不言举傅说之事。如前章之阿衡何欤。
臣璧对曰。四方之极。犹言四方之表。极字如北极屋极之极。高宗以不敢怠荒之心。建极于上。以不僭不滥之政。敷极于下。而自西自东。自南自北。莫不取正于邦畿。则是所谓会极归极也。下文赫赫厥声。濯濯厥灵。何莫非颂尔极者耶。至如高宗之有傅说。犹汤之有伊尹。祭高宗之时。傅说必从与享之。罔俾阿衡
质庵集卷之四 第 1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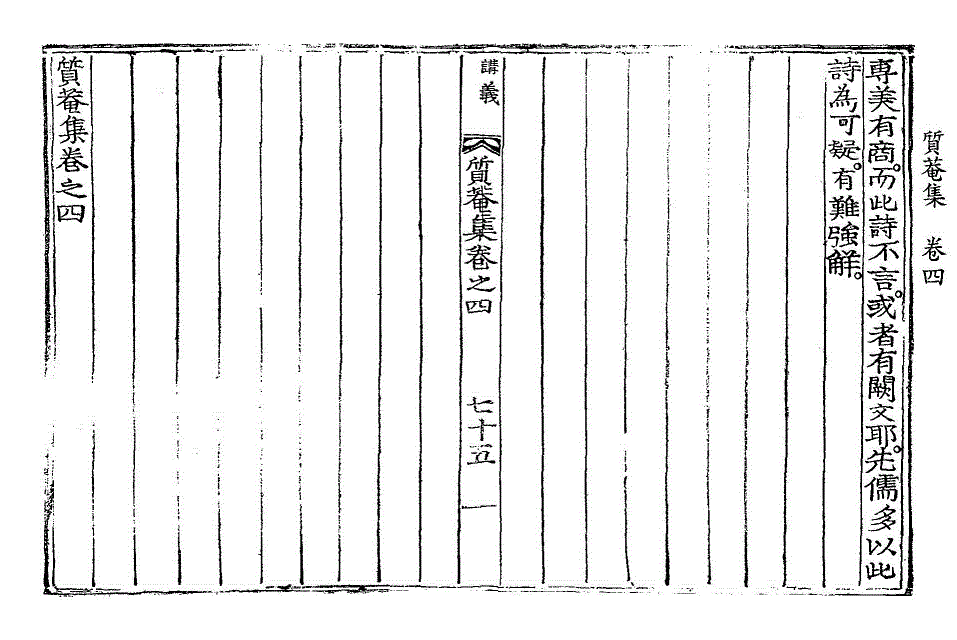 专美有商。而此诗不言。或者有阙文耶。先儒多以此诗为可疑。有难强解。
专美有商。而此诗不言。或者有阙文耶。先儒多以此诗为可疑。有难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