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质庵集卷之三 第 x 页
质庵集卷之三(奎章阁内制)
讲义(诗传上)
讲义(诗传上)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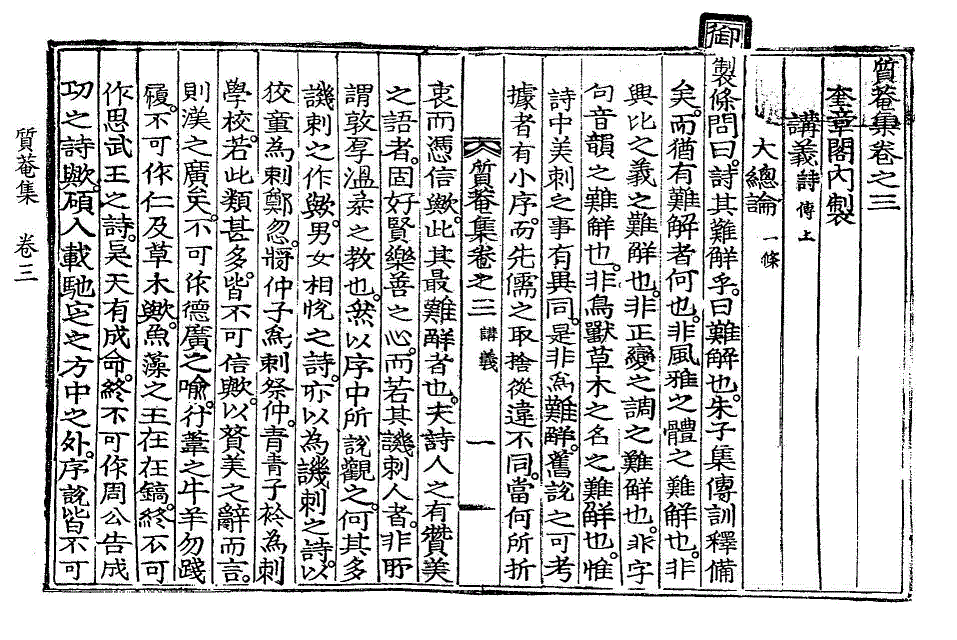 大总论(一条)
大总论(一条)御制条问曰。诗其难解乎。曰难解也。朱子集传训释备矣。而犹有难解者何也。非风雅之体之难解也。非兴比之义之难解也。非正变之调之难解也。非字句音韵之难解也。非鸟兽草木之名之难解也。惟诗中美刺之事有异同。是非为难解旧说之可考据者有小序。而先儒之取舍从违不同。当何所折衷而凭信欤。此其最难解者也。夫诗人之有赞美之语者。固好贤乐善之心。而若其讥刺人者。非所谓敦厚温柔之教也。然以序中所说观之。何其多讥刺之作欤。男女相悦之诗。亦以为讥刺之诗。以狡童为刺郑忽。将仲子为刺祭仲。青青子衿为刺学校。若此类甚多。皆不可信欤。以赞美之辞而言。则汉之广矣。不可作德广之喻。行苇之牛羊勿践履。不可作仁及草木欤。鱼藻之王在在镐。终不可作思武王之诗。昊天有成命。终不可作周公告成功之诗欤。硕人载驰定之方中之外。序说皆不可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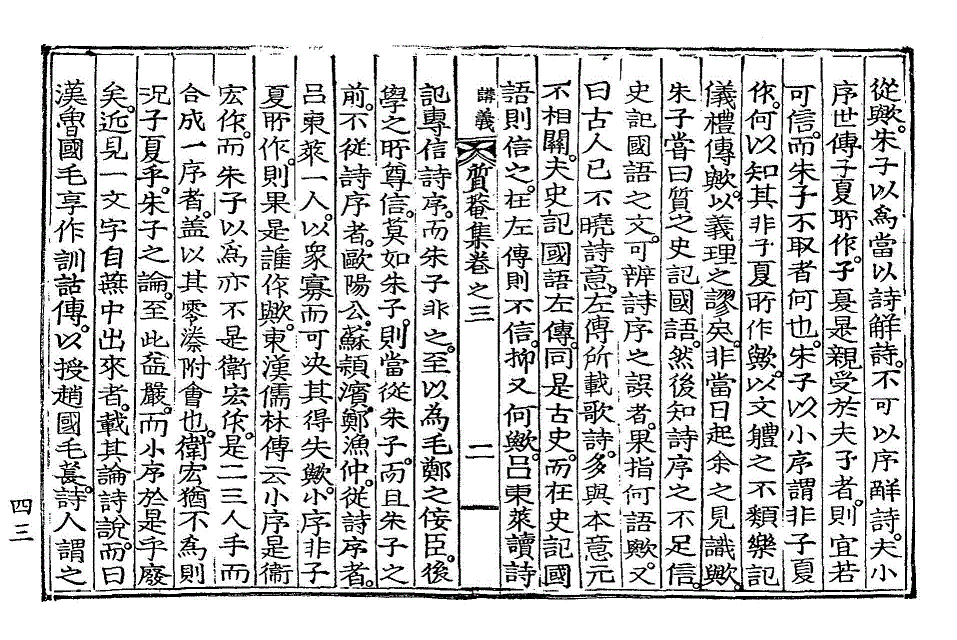 从欤。朱子以为当以诗解诗。不可以序解诗。夫小序世传子夏所作。子夏是亲受于夫子者。则宜若可信。而朱子不取者何也。朱子以小序谓非子夏作。何以知其非子夏所作欤。以文体之不类乐记仪礼传欤。以义理之谬戾。非当日起余之见识欤。朱子尝曰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不足信。史记国语之文。可辨诗序之误者。果指何语欤。又曰古人已不晓诗意。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夫史记国语左传。同是古史。而在史记国语则信之。在左传则不信。抑又何欤。吕东莱读诗记专信诗序。而朱子非之。至以为毛郑之佞臣。后学之所尊信。莫如朱子。则当从朱子。而且朱子之前。不从诗序者。欧阳公,苏颖滨,郑渔仲。从诗序者。吕东莱一人。以众寡而可决其得失欤。小序非子夏所作。则果是谁作欤。东汉儒林传云小序是卫宏作。而朱子以为亦不是卫宏作。是二三人手而合成一序者。盖以其零溱附会也。卫宏犹不为则况子夏乎。朱子之论。至此益严。而小序于是乎废矣。近见一文字自燕中出来者。载其论诗说。而曰汉鲁国毛享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诗人谓之
从欤。朱子以为当以诗解诗。不可以序解诗。夫小序世传子夏所作。子夏是亲受于夫子者。则宜若可信。而朱子不取者何也。朱子以小序谓非子夏作。何以知其非子夏所作欤。以文体之不类乐记仪礼传欤。以义理之谬戾。非当日起余之见识欤。朱子尝曰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不足信。史记国语之文。可辨诗序之误者。果指何语欤。又曰古人已不晓诗意。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夫史记国语左传。同是古史。而在史记国语则信之。在左传则不信。抑又何欤。吕东莱读诗记专信诗序。而朱子非之。至以为毛郑之佞臣。后学之所尊信。莫如朱子。则当从朱子。而且朱子之前。不从诗序者。欧阳公,苏颖滨,郑渔仲。从诗序者。吕东莱一人。以众寡而可决其得失欤。小序非子夏所作。则果是谁作欤。东汉儒林传云小序是卫宏作。而朱子以为亦不是卫宏作。是二三人手而合成一序者。盖以其零溱附会也。卫宏犹不为则况子夏乎。朱子之论。至此益严。而小序于是乎废矣。近见一文字自燕中出来者。载其论诗说。而曰汉鲁国毛享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诗人谓之质庵集卷之三 第 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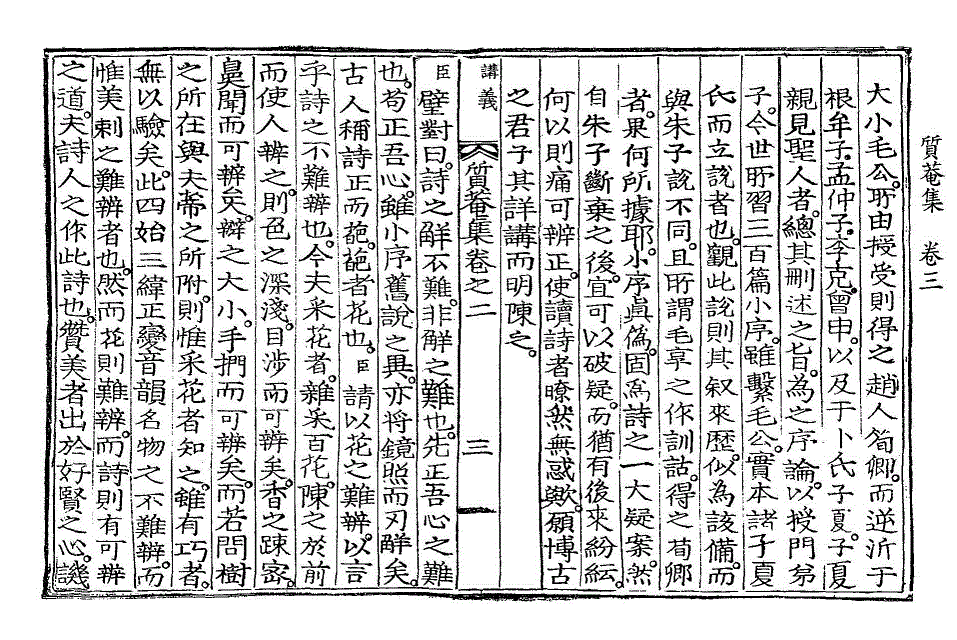 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则得之赵人笋(一作荀)卿。而逆沂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于卜氏子夏。子夏亲见圣人者。总其删述之旨。为之序论。以授门弟子。今世所习三百篇小序。虽系毛公。实本诸子夏氏而立说者也。观此说则其叙来历。似为该备。而与朱子说不同。且所谓毛享之作训诂。得之荀卿者。果何所据耶。小序真伪。固为诗之一大疑案。然自朱子断弃之后。宜可以破疑。而犹有后来纷纭。何以则痛可辨正。使读诗者暸然无惑欤。愿博古之君子其详讲而明陈之。
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则得之赵人笋(一作荀)卿。而逆沂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于卜氏子夏。子夏亲见圣人者。总其删述之旨。为之序论。以授门弟子。今世所习三百篇小序。虽系毛公。实本诸子夏氏而立说者也。观此说则其叙来历。似为该备。而与朱子说不同。且所谓毛享之作训诂。得之荀卿者。果何所据耶。小序真伪。固为诗之一大疑案。然自朱子断弃之后。宜可以破疑。而犹有后来纷纭。何以则痛可辨正。使读诗者暸然无惑欤。愿博古之君子其详讲而明陈之。臣璧对曰。诗之解不难。非解之难也。先正吾心之难也。苟正吾心。虽小序旧说之异。亦将镜照而刃解矣。古人称诗正而葩。葩者花也。臣请以花之难辨。以言乎诗之不难辨也。今夫采花者。杂采百花。陈之于前而使人辨之。则色之深浅。目涉而可辨矣。香之疏密。鼻闻而可辨矣。瓣之大小。手扪而可辨矣。而若问树之所在与夫蒂之所附。则惟采花者知之。虽有巧者。无以验矣。此四始三纬正变音韵名物之不难辨。而惟美刺之难辨者也。然而花则难辨。而诗则有可辨之道。夫诗人之作此诗也。赞美者出于好贤之心。讥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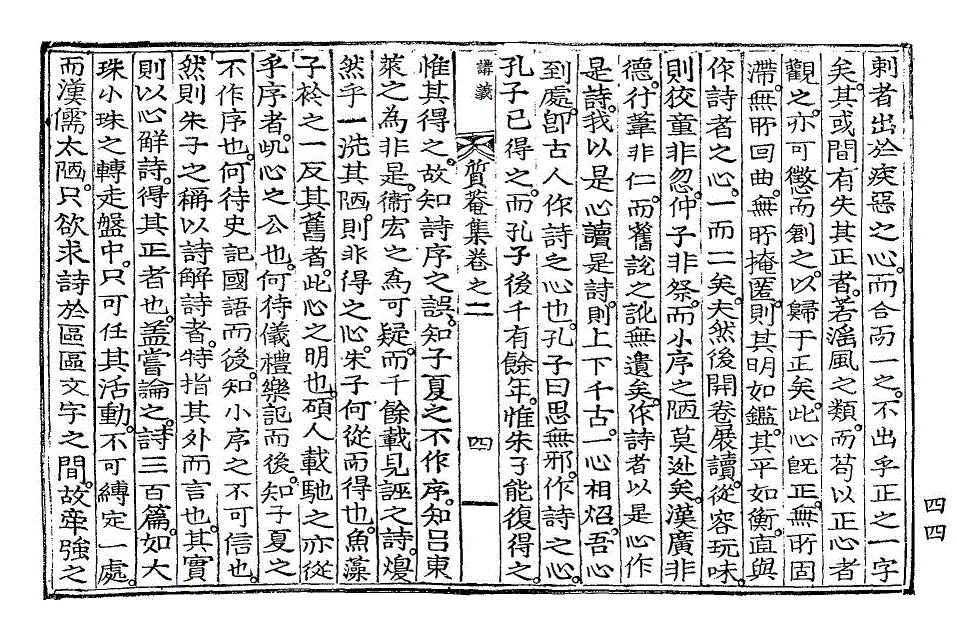 刺者出于疾恶之心。而合而一之。不出乎正之一字矣。其或间有失其正者。若淫风之类。而苟以正心者观之。亦可惩而创之。以归于正矣。此心既正。无所固滞。无所回曲。无所掩匿。则其明如鉴。其平如衡。直与作诗者之心。一而二矣。夫然后开卷展读。从容玩味。则狡童非忽。仲子非祭。而小序之陋莫逃矣。汉广非德。行苇非仁。而旧说之讹无遗矣。作诗者以是心作是诗。我以是心读是诗。则上下千古。一心相炤。吾心到处。即古人作诗之心也。孔子曰思无邪。作诗之心。孔子已得之。而孔子后千有馀年。惟朱子能复得之。惟其得之。故知诗序之误。知子夏之不作序。知吕东莱之为非是。卫宏之为可疑。而千馀载见诬之诗。焕然乎一洗其陋。则非得之心。朱子何从而得也。鱼藻子衿之一反其旧者。此心之明也。硕人载驰之亦从乎序者。此心之公也。何待仪礼乐记而后。知子夏之不作序也。何待史记国语而后。知小序之不可信也。然则朱子之称以诗解诗者。特指其外而言也。其实则以心解诗。得其正者也。盖尝论之。诗三百篇。如大珠小珠之转走盘中。只可任其活动。不可缚定一处。而汉儒太陋。只欲求诗于区区文字之间。故牵强之
刺者出于疾恶之心。而合而一之。不出乎正之一字矣。其或间有失其正者。若淫风之类。而苟以正心者观之。亦可惩而创之。以归于正矣。此心既正。无所固滞。无所回曲。无所掩匿。则其明如鉴。其平如衡。直与作诗者之心。一而二矣。夫然后开卷展读。从容玩味。则狡童非忽。仲子非祭。而小序之陋莫逃矣。汉广非德。行苇非仁。而旧说之讹无遗矣。作诗者以是心作是诗。我以是心读是诗。则上下千古。一心相炤。吾心到处。即古人作诗之心也。孔子曰思无邪。作诗之心。孔子已得之。而孔子后千有馀年。惟朱子能复得之。惟其得之。故知诗序之误。知子夏之不作序。知吕东莱之为非是。卫宏之为可疑。而千馀载见诬之诗。焕然乎一洗其陋。则非得之心。朱子何从而得也。鱼藻子衿之一反其旧者。此心之明也。硕人载驰之亦从乎序者。此心之公也。何待仪礼乐记而后。知子夏之不作序也。何待史记国语而后。知小序之不可信也。然则朱子之称以诗解诗者。特指其外而言也。其实则以心解诗。得其正者也。盖尝论之。诗三百篇。如大珠小珠之转走盘中。只可任其活动。不可缚定一处。而汉儒太陋。只欲求诗于区区文字之间。故牵强之质庵集卷之三 第 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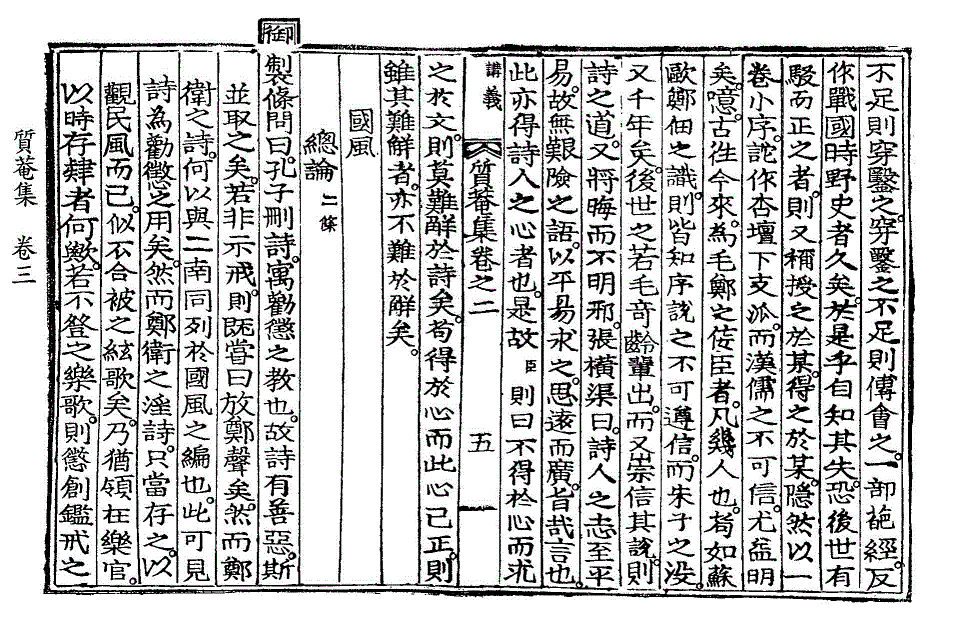 不足则穿凿之。穿凿之不足则傅会之。一部葩经。反作战国时野史者久矣。于是乎自知其失。恐后世有驳而正之者。则又称授之于某。得之于某。隐然以一卷小序。詑作杏坛下支派。而汉儒之不可信。尤益明矣。噫。古往今来。为毛郑之佞臣者。凡几人也。苟如苏欧郑佃之识。则皆知序说之不可遵信。而朱子之没。又千年矣。后世之若毛奇龄辈出。而又崇信其说。则诗之道。又将晦而不明邪。张横渠曰。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语。以平易求之。思远而广。旨哉言也。此亦得诗人之心者也。是故臣则曰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文。则莫难解于诗矣。苟得于心而此心已正。则虽其难解者。亦不难于解矣。
不足则穿凿之。穿凿之不足则傅会之。一部葩经。反作战国时野史者久矣。于是乎自知其失。恐后世有驳而正之者。则又称授之于某。得之于某。隐然以一卷小序。詑作杏坛下支派。而汉儒之不可信。尤益明矣。噫。古往今来。为毛郑之佞臣者。凡几人也。苟如苏欧郑佃之识。则皆知序说之不可遵信。而朱子之没。又千年矣。后世之若毛奇龄辈出。而又崇信其说。则诗之道。又将晦而不明邪。张横渠曰。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语。以平易求之。思远而广。旨哉言也。此亦得诗人之心者也。是故臣则曰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文。则莫难解于诗矣。苟得于心而此心已正。则虽其难解者。亦不难于解矣。国风
总论(二条)
御制条问曰。孔子删诗。寓劝惩之教也。故诗有善恶。斯并取之矣。若非示戒。则既尝曰放郑声矣。然而郑卫之诗。何以与二南同列于国风之编也。此可见诗为劝惩之用矣。然而郑卫之淫诗。只当存之。以观民风而已。似不合被之弦歌矣。乃犹领在乐官。以时存肄者何欤。若不登之乐歌。则惩创鉴戒之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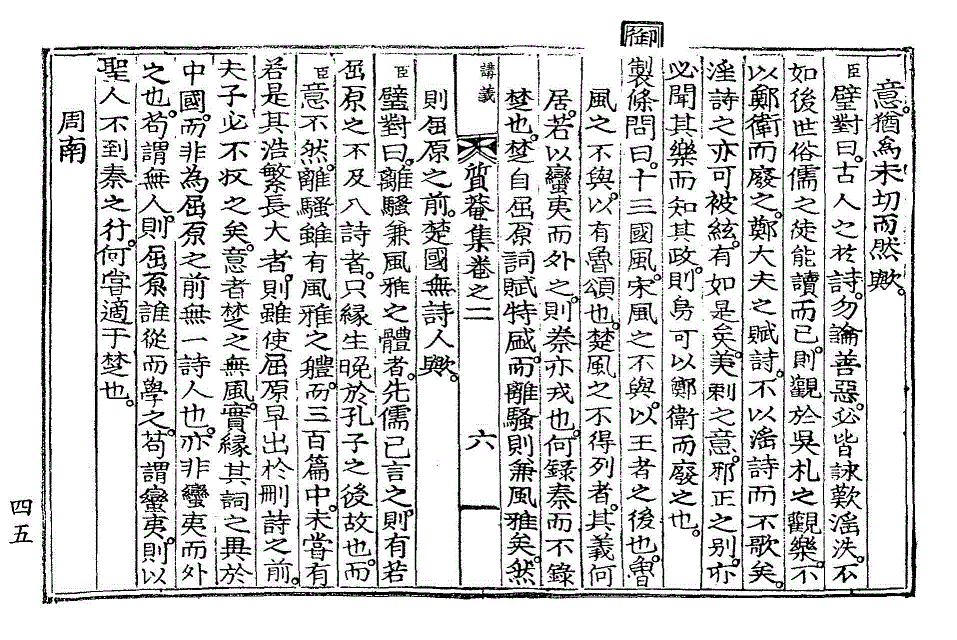 意。犹为未切而然欤。
意。犹为未切而然欤。臣璧对曰。古人之于诗。勿论善恶。必皆咏叹淫泆。不如后世俗儒之徒能读而已。则观于吴札之观乐。不以郑卫而废之。郑大夫之赋诗。不以淫诗而不歌矣。淫诗之亦可被弦。有如是矣。美刺之意。邪正之别。亦必闻其乐而知其政。则乌可以郑卫而废之也。
御制条问曰。十三国风。宋风之不与。以王者之后也。鲁风之不与。以有鲁颂也。楚风之不得列者。其义何居。若以蛮夷而外之。则秦亦戎也。何录秦而不录楚也。楚自屈原词赋特盛。而离骚则兼风雅矣。然则屈原之前。楚国无诗人欤。
臣璧对曰。离骚兼风雅之体者。先儒已言之。则有若屈原之不及入诗者。只缘生晚于孔子之后故也。而臣意不然。离骚虽有风雅之体。而三百篇中。未尝有若是其浩繁长大者。则虽使屈原早出于删诗之前。夫子必不收之矣。意者楚之无风。实缘其词之异于中国。而非为屈原之前无一诗人也。亦非蛮夷而外之也。苟谓无人。则屈原谁从而学之。苟谓蛮夷。则以圣人不到秦之行。何尝适于楚也。
周南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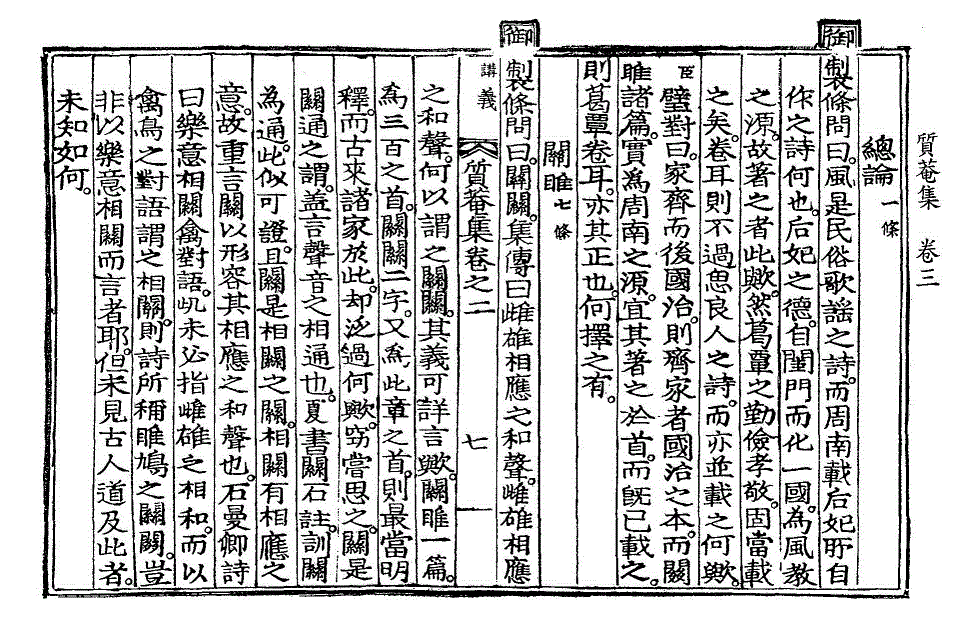 总论(一条)
总论(一条)御制条问曰。风是民俗歌谣之诗。而周南载后妃所自作之诗何也。后妃之德。自闺门而化一国。为风教之源。故著之者此欤。然葛覃之勤俭孝敬。固当载之矣。卷耳则不过思良人之诗。而亦并载之何欤。
臣璧对曰家齐而后国治。则齐家者国治之本。而关雎诸篇。实为周南之源。宜其著之于首。而既已载之。则葛覃卷耳。亦其正也。何择之有。
关雎(七条)
御制条问曰。关关。集传曰雌雄相应之和声。雌雄相应之和声。何以谓之关关。其义可详言欤。关雎一篇。为三百之首。关关二字。又为此章之首。则最当明释。而古来诸家于此。却泛过何欤。窃尝思之。关是关通之谓。盖言声音之相通也。夏书关石注。训关为通。此似可證。且关是相关之关。相关有相应之意。故重言关以形容其相应之和声也。石曼卿诗曰乐意相关禽对语。此未必指雌雄之相和。而以禽鸟之对语谓之相关。则诗所称雎鸠之关关。岂非以乐意相关而言者耶。但未见古人道及此者。未知如何。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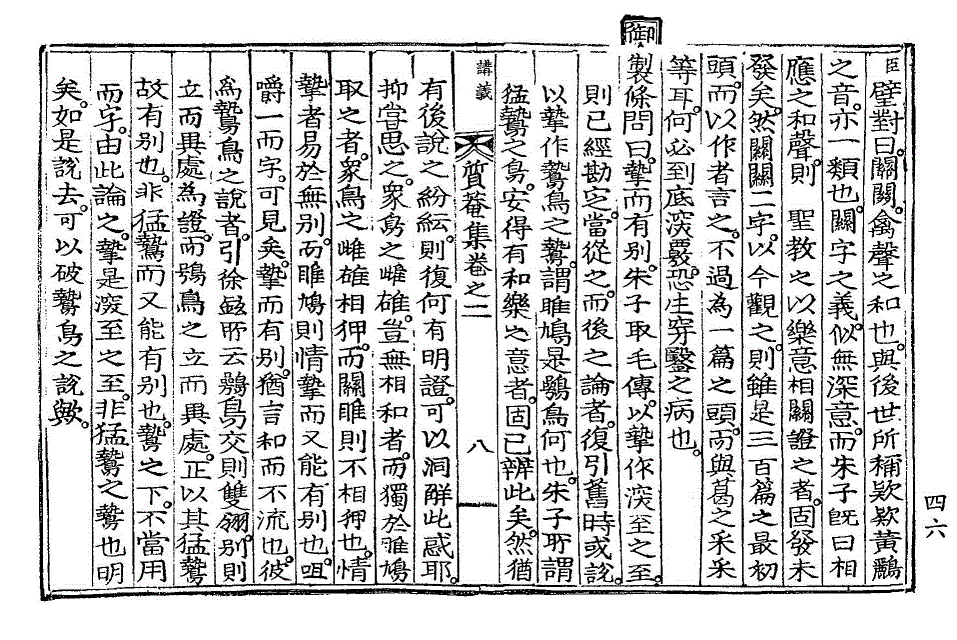 臣璧对曰。关关。禽声之和也。与后世所称款款黄鹂之音。亦一类也。关字之义。似无深意。而朱子既曰相应之和声。则 圣教之以乐意相关證之者。固发未发矣。然关关二字。以今观之。则虽是三百篇之最初头。而以作者言之。不过为一篇之头。而与葛之采采等耳。何必到底深覈。恐生穿凿之病也。
臣璧对曰。关关。禽声之和也。与后世所称款款黄鹂之音。亦一类也。关字之义。似无深意。而朱子既曰相应之和声。则 圣教之以乐意相关證之者。固发未发矣。然关关二字。以今观之。则虽是三百篇之最初头。而以作者言之。不过为一篇之头。而与葛之采采等耳。何必到底深覈。恐生穿凿之病也。御制条问曰。挚而有别。朱子取毛传。以挚作深至之至。则已经勘定。当从之。而后之论者。复引旧时或说。以挚作鸷鸟之鸷。谓雎鸠是鹗鸟何也。朱子所谓猛鸷之鸟。安得有和乐之意者。固已辨此矣。然犹有后说之纷纭。则复何有明證。可以洞解此惑耶。抑尝思之。众鸟之雌雄。岂无相和者。而独于雎鸠取之者。众鸟之雌雄相狎。而关雎则不相狎也。情挚者易于无别。而雎鸠则情挚而又能有别也。咀嚼一而字。可见矣。挚而有别。犹言和而不流也。彼为鸷鸟之说者。引徐铉所云鹗鸟交则双翎。别则立而异处为證。而鸮鸟之立而异处。正以其猛鸷故有别也。非猛鸷而又能有别也。鸷之下。不当用而字。由此论之。挚是深至之至。非猛鸷之鸷也明矣。如是说去。可以破鸷鸟之说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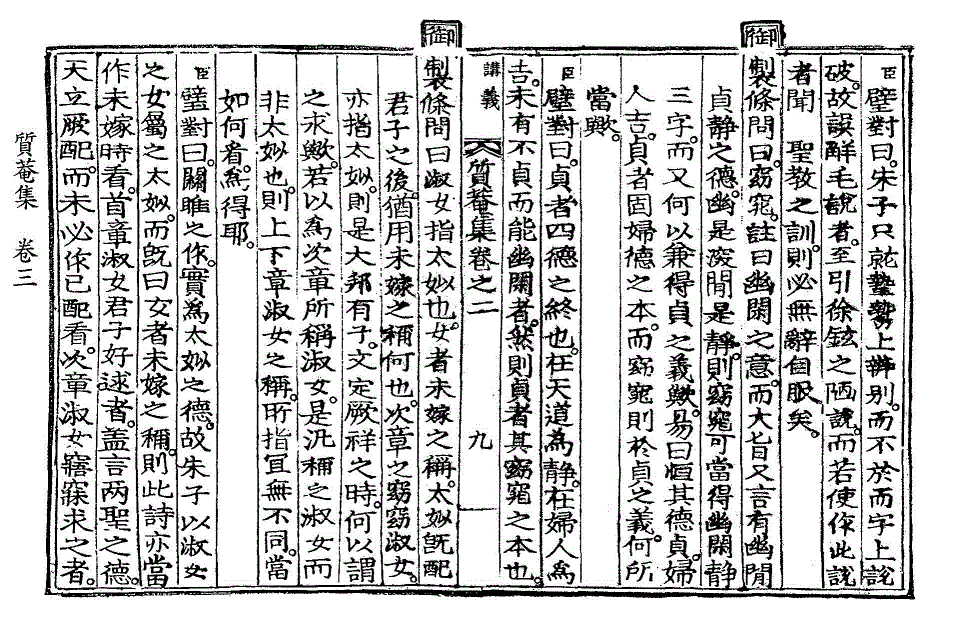 臣璧对曰。朱子只就挚鸷上辨别。而不于而字上说破。故误解毛说者。至引徐铉之陋说。而若使作此说者闻 圣教之训。则必无辞自服矣。
臣璧对曰。朱子只就挚鸷上辨别。而不于而字上说破。故误解毛说者。至引徐铉之陋说。而若使作此说者闻 圣教之训。则必无辞自服矣。御制条问曰。窈窕。注曰幽闲之意。而大旨又言有幽閒贞静之德。幽是深閒是静。则窈窕可当得幽闲静三字。而又何以兼得贞之义欤。易曰恒其德贞。妇人吉。贞者固妇德之本。而窈窕则于贞之义。何所当欤。
臣璧对曰。贞者四德之终也。在天道为静。在妇人为吉。未有不贞而能幽闲者。然则贞者其窈窕之本也。
御制条问曰淑女指太姒也。女者未嫁之称。太姒既配君子之后。犹用未嫁之称何也。次章之窈窈淑女。亦指太姒。则是大邦有子。文定厥祥之时。何以谓之求欤。若以为次章所称淑女。是汎称之淑女而非太姒也。则上下章淑女之称。所指宜无不同。当如何看。为得耶。
臣璧对曰。关雎之作。实为太姒之德。故朱子以淑女之女属之太姒。而既曰女者未嫁之称。则此诗亦当作未嫁时看。首章淑女君子好逑者。盖言两圣之德。天立厥配。而未必作已配看。次章淑女寤寐求之者。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7L 页
 言其求之之时。而亦未必舟梁已迎之后也。至三章然后钟鼓琴瑟之淑女。方是已嫁之女也。似有嫌于称女。而此其始至之初也。新归之妇。犹称以女者。魏风亦有其例。则称女亦通。臣谓关雎三章。称太姒谓淑女者。无所不可矣。
言其求之之时。而亦未必舟梁已迎之后也。至三章然后钟鼓琴瑟之淑女。方是已嫁之女也。似有嫌于称女。而此其始至之初也。新归之妇。犹称以女者。魏风亦有其例。则称女亦通。臣谓关雎三章。称太姒谓淑女者。无所不可矣。御制条问曰。君子指文王也。君子即妇人谓夫之称。如殷其雷之振振君子。汝坟之既见君子是也。诗虽宫人所作。而从太姒说。故称文王为君子。而或引旱麓之岂弟君子。以为是指人君之称。则此有不然者。文王之聘姒氏。是为世子时也。何得遽以人君之称称之也。按戴记。文王九十七而终。书之无逸曰文王之享国五十年。则文王四十八始即位。为西伯也。文王年十三。生伯邑考。其聘姒氏。当时十馀岁时也。当是日三朝王季之时也。古果有称贰君为君子之文否。未之见也。则何可以此君子与旱麓之君子同看耶。匡衡所谓配至尊而为宗庙主者。亦指方来说也。非谓已成君也。若以为文王即位之后。追叙其婚姻之初。则大旨所谓宫中之人。于其始至云者。岂误耶。以此论之。或说不可从。未知如何。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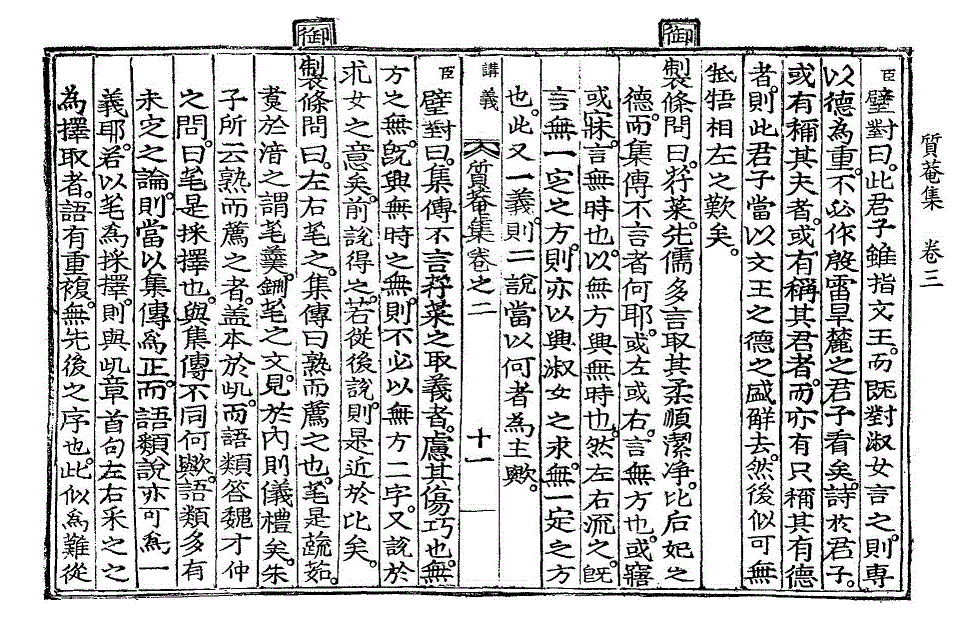 臣璧对曰。此君子虽指文王。而既对淑女言之。则专以德为重。不必作殷雷旱麓之君子看矣。诗于君子。或有称其夫者。或有称其君者。而亦有只称其有德者。则此君子当以文王之德之盛解去。然后似可无牴牾相左之叹矣。
臣璧对曰。此君子虽指文王。而既对淑女言之。则专以德为重。不必作殷雷旱麓之君子看矣。诗于君子。或有称其夫者。或有称其君者。而亦有只称其有德者。则此君子当以文王之德之盛解去。然后似可无牴牾相左之叹矣。御制条问曰。荇菜。先儒多言取其柔顺洁净。比后妃之德。而集传不言者何耶。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或寤或寐。言无时也。以无方兴无时也。然左右流之。既言无一定之方。则亦以兴淑女之求。无一定之方也。此又一义。则二说当以何者为主欤。
臣璧对曰。集传不言荇菜之取义者。虑其伤巧也。无方之无。既兴无时之无。则不必以无方二字。又说于求女之意矣。前说得之。若从后说。则是近于比矣。
御制条问曰。左右芼之。集传曰熟而荐之也。芼是蔬茹。煮于湆之谓芼羹。铏芼之文。见于内则仪礼矣。朱子所云熟而荐之者。盖本于此。而语类答魏才仲之问。曰芼是采择也。与集传不同何欤。语类多有未定之论。则当以集传为正。而语类说亦可为一义耶。若以芼为采择。则与此章首句左右采之之为择取者。语有重复。无先后之序也。此似为难从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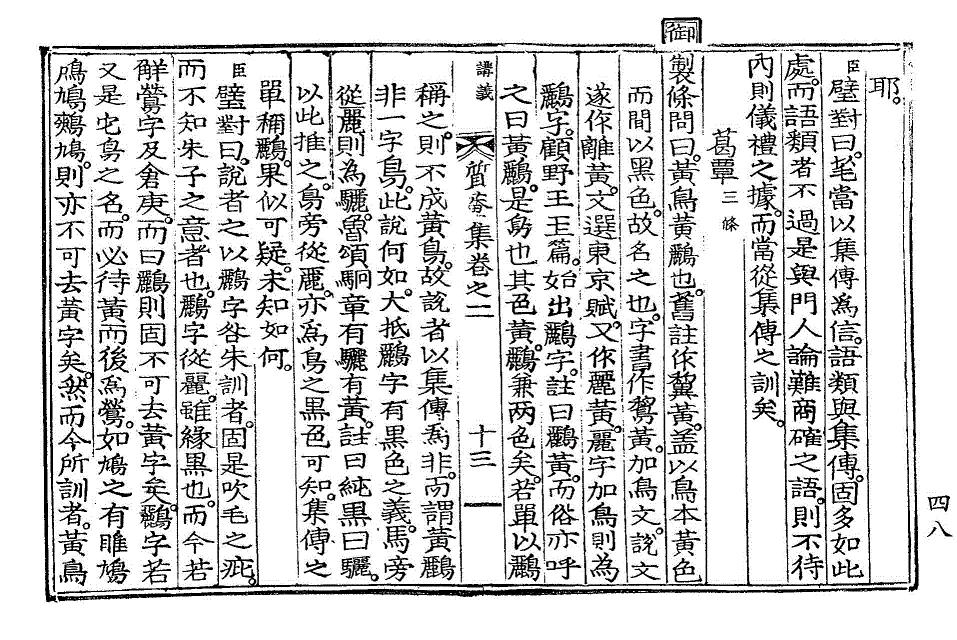 耶。
耶。臣璧对曰。芼当以集传为信。语类与集传。固多如此处。而语类者不过是与门人论难商确之语。则不待内则仪礼之据。而当从集传之训矣。
葛覃(三条)
御制条问曰。黄鸟黄鹂也。旧注作
臣璧对曰。说者之以鹂字咎朱训者。固是吹毛之疵。而不知朱子之意者也。鹂字从丽。虽缘黑也。而今若解莺字及仓庚。而曰鹂则固不可去黄字矣。鹂字若又是它鸟之名。而必待黄而后为莺。如鸠之有雎鸠鸤鸠鹴鸠。则亦不可去黄字矣。然而今所训者。黄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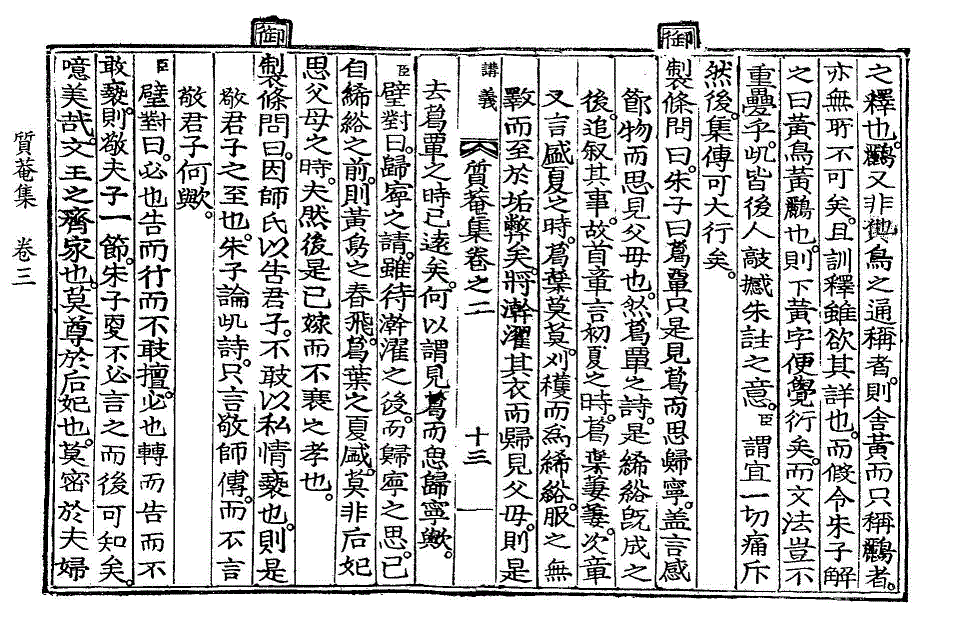 之释也。鹂又非他鸟之通称者。则舍黄而只称鹂者。亦无所不可矣。且训释虽欲其详也。而假令朱子解之曰黄鸟黄鹂也。则下黄字便觉衍矣。而文法岂不重叠乎。此皆后人敲撼朱注之意。臣谓宜一切痛斥然后。集传可大行矣。
之释也。鹂又非他鸟之通称者。则舍黄而只称鹂者。亦无所不可矣。且训释虽欲其详也。而假令朱子解之曰黄鸟黄鹂也。则下黄字便觉衍矣。而文法岂不重叠乎。此皆后人敲撼朱注之意。臣谓宜一切痛斥然后。集传可大行矣。御制条问曰。朱子曰葛覃只是见葛而思归宁。盖言感节物而思见父母也。然葛覃之诗。是絺绤既成之后。追叙其事。故首章言初夏之时。葛叶萋萋。次章又言盛夏之时。葛叶莫莫。刈穫而为絺绤。服之无斁而至于垢弊矣。将浣濯其衣而归见父母。则是去葛覃之时已远矣。何以谓见葛而思归宁欤。
臣璧对曰。归宁之请。虽待浣濯之后。而归宁之思。已自絺绤之前。则黄鸟之春飞。葛叶之夏盛。莫非后妃思父母之时。夫然后是已嫁而不衰之孝也。
御制条问曰。因师氏以告君子。不敢以私情亵也。则是敬君子之至也。朱子论此诗。只言敬师傅。而不言敬君子何欤。
臣璧对曰。必也告而行而不敢擅。必也转而告而不敢亵。则敬夫子一节。朱子更不必言之而后可知矣。噫美哉。文王之齐家也。莫尊于后妃也。莫密于夫妇
质庵集卷之三 第 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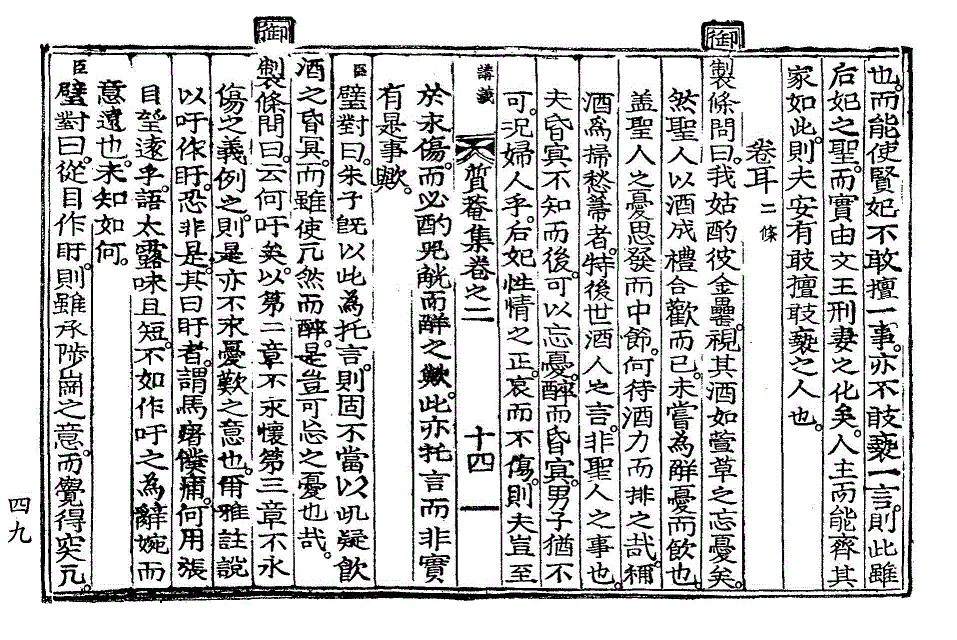 也。而能使贤妃不敢擅一事。亦不敢亵一言。则此虽后妃之圣。而实由文王刑妻之化矣。人主而能齐其家如此。则夫安有敢擅敢亵之人也。
也。而能使贤妃不敢擅一事。亦不敢亵一言。则此虽后妃之圣。而实由文王刑妻之化矣。人主而能齐其家如此。则夫安有敢擅敢亵之人也。卷耳(二条)
御制条问曰。我姑酌彼金罍。视其酒如萱草之忘忧矣。然圣人以酒成礼合欢而已。未尝为解忧而饮也。盖圣人之忧思发而中节。何待酒力而排之哉。称酒为扫愁帚者。特后世酒人之言。非圣人之事也。夫昏冥不知而后。可以忘忧。醉而昏冥。男子犹不可。况妇人乎。后妃性情之正。哀而不伤。则夫岂至于永伤。而必酌兕觥而解之欤。此亦托言而非实有是事欤。
臣璧对曰。朱子既以此为托言。则固不当以此疑饮酒之昏冥。而虽使兀然而醉。是岂可忘之忧也哉。
御制条问曰。云何吁矣。以第二章不永怀第三章不永伤之义例之。则是亦不永忧叹之意也。尔雅注说以吁作盱。恐非是。其曰盱者。谓马瘏仆痡。何用张目望远乎。语太露味且短。不如作吁之为辞婉而意远也。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从目作盱。则虽承陟岗之意。而觉得突兀。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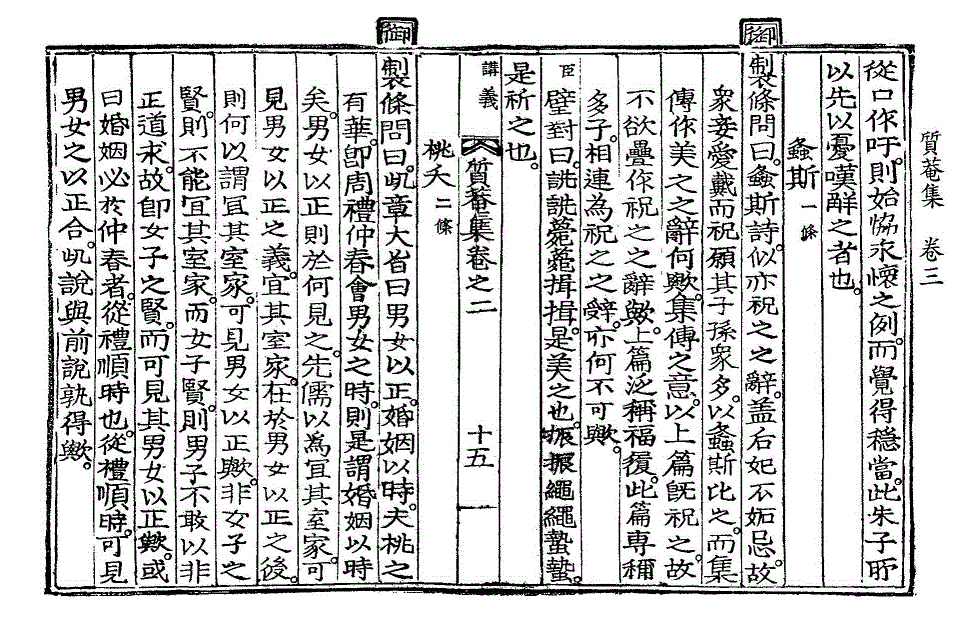 从口作吁。则始协永怀之例。而觉得稳当。此朱子所以先以忧叹解之者也。
从口作吁。则始协永怀之例。而觉得稳当。此朱子所以先以忧叹解之者也。螽斯(一条)
御制条问曰。螽斯诗。似亦祝之之辞。盖后妃不妒忌。故众妾爱戴而祝愿其子孙众多。以螽斯比之。而集传作美之之辞何欤。集传之意。以上篇既祝之。故不欲叠作祝之之辞欤。上篇泛称福履。此篇专称多子。相连为祝之之辞。亦何不可欤。
臣璧对曰。诜诜薨薨揖揖。是美之也。振振绳绳蛰蛰。是祈之也。
桃夭(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章大旨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夫桃之有华。即周礼仲春会男女之时。则是谓婚姻以时矣。男女以正则于何见之。先儒以为宜其室家。可见男女以正之义。宜其室家。在于男女以正之后。则何以谓宜其室家。可见男女以正欤。非女子之贤。则不能宜其室家。而女子贤。则男子不敢以非正道求。故即女子之贤。而可见其男女以正欤。或曰婚姻必于仲春者。从礼顺时也。从礼顺时。可见男女之以正合。此说与前说孰得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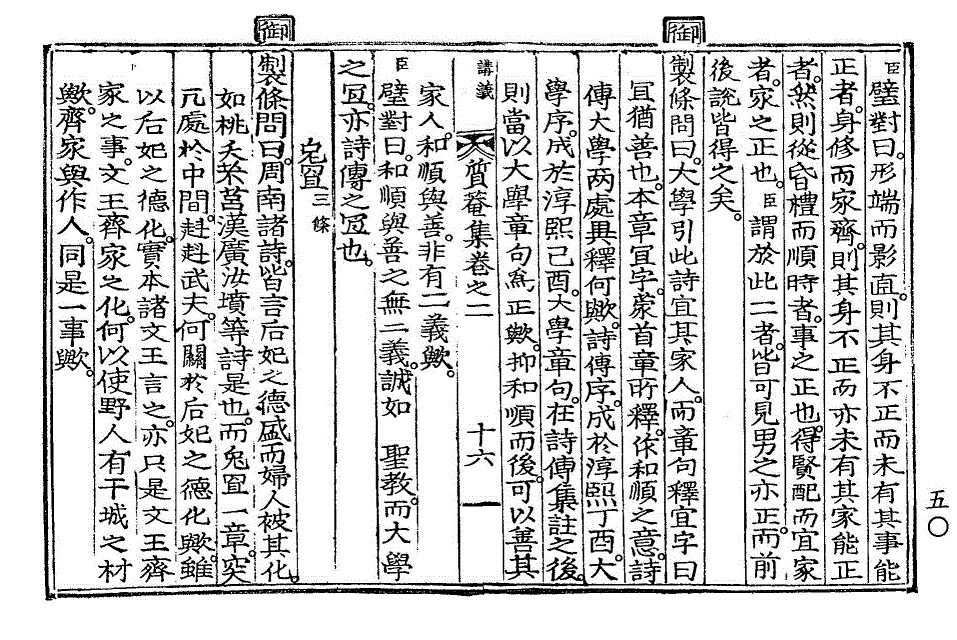 臣璧对曰。形端而影直。则其身不正而未有其事能正者。身修而家齐。则其身不正而亦未有其家能正者。然则从昏礼而顺时者。事之正也。得贤配而宜家者。家之正也。臣谓于此二者。皆可见男之亦正。而前后说皆得之矣。
臣璧对曰。形端而影直。则其身不正而未有其事能正者。身修而家齐。则其身不正而亦未有其家能正者。然则从昏礼而顺时者。事之正也。得贤配而宜家者。家之正也。臣谓于此二者。皆可见男之亦正。而前后说皆得之矣。御制条问曰。大学引此诗宜其家人。而章句释宜字曰宜犹善也。本章宜字。蒙首章所释。作和顺之意。诗传大学两处异释何欤。诗传序。成于淳熙丁酉。大学序。成于淳熙己酉。大学章句。在诗传集注之后。则当以大学章句为正欤。抑和顺而后。可以善其家人。和顺与善。非有二义欤。
臣璧对曰。和顺与善之无二义。诚如 圣教。而大学之宜。亦诗传之宜也。
兔罝(三条)
御制条问曰。周南诸诗。皆言后妃之德盛而妇人被其化。如桃夭芣莒汉广汝坟等诗是也。而兔罝一章。突兀处于中间。赳赳武夫。何关于后妃之德化欤。虽以后妃之德化。实本诸文王言之。亦只是文王齐家之事。文王齐家之化。何以使野人有干城之材欤。齐家与作人。同是一事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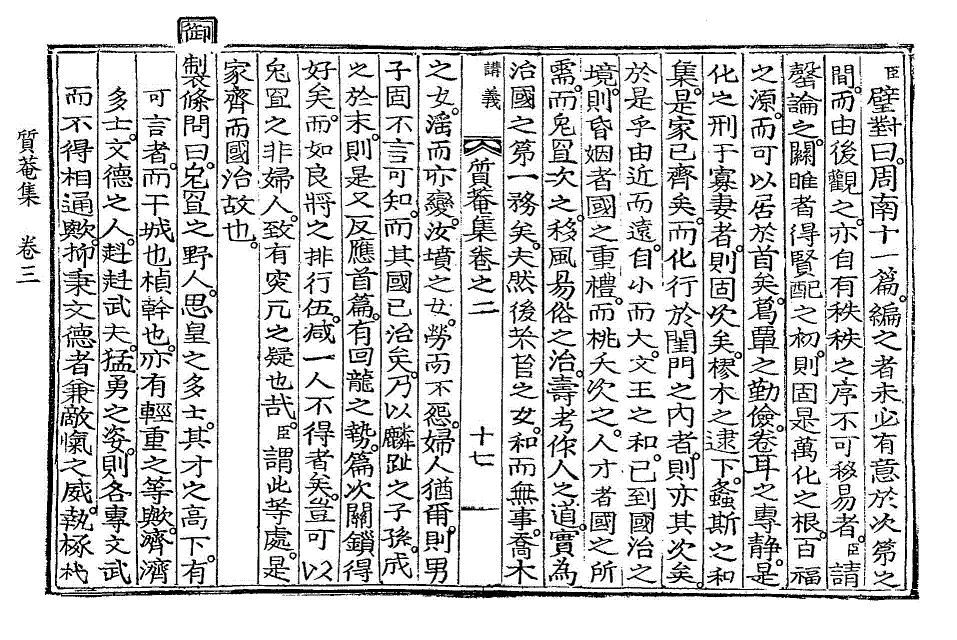 臣璧对曰。周南十一篇。编之者未必有意于次第之间。而由后观之。亦自有秩秩之序不可移易者。臣请罄论之。关雎者得贤配之初。则固是万化之根。百福之源。而可以居于首矣。葛覃之勤俭。卷耳之专静。是化之刑于寡妻者。则固次矣。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和集。是家已齐矣。而化行于闺门之内者。则亦其次矣。于是乎由近而远。自小而大。文王之和。已到国治之境。则昏姻者国之重礼。而桃夭次之。人才者国之所需。而兔罝次之。移风易俗之治。寿考作人之道。实为治国之第一务矣。夫然后芣苢之女。和而无事。乔木之女。淫而亦变。汝坟之女。劳而不怨。妇人犹尔。则男子固不言可知。而其国已治矣。乃以麟趾之子孙。成之于末。则是又反应首篇。有回龙之势。篇次关锁得好矣。而如良将之排行伍。减一人不得者矣。岂可以兔罝之非妇人。致有突兀之疑也哉。臣谓此等处。是家齐而国治故也。
臣璧对曰。周南十一篇。编之者未必有意于次第之间。而由后观之。亦自有秩秩之序不可移易者。臣请罄论之。关雎者得贤配之初。则固是万化之根。百福之源。而可以居于首矣。葛覃之勤俭。卷耳之专静。是化之刑于寡妻者。则固次矣。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和集。是家已齐矣。而化行于闺门之内者。则亦其次矣。于是乎由近而远。自小而大。文王之和。已到国治之境。则昏姻者国之重礼。而桃夭次之。人才者国之所需。而兔罝次之。移风易俗之治。寿考作人之道。实为治国之第一务矣。夫然后芣苢之女。和而无事。乔木之女。淫而亦变。汝坟之女。劳而不怨。妇人犹尔。则男子固不言可知。而其国已治矣。乃以麟趾之子孙。成之于末。则是又反应首篇。有回龙之势。篇次关锁得好矣。而如良将之排行伍。减一人不得者矣。岂可以兔罝之非妇人。致有突兀之疑也哉。臣谓此等处。是家齐而国治故也。御制条问曰。兔罝之野人。思皇之多士。其才之高下。有可言者。而干城也桢干也。亦有轻重之等欤。济济多士。文德之人。赳赳武夫。猛勇之姿。则各专文武而不得相通欤。抑秉文德者兼敌忾之威。执椓杙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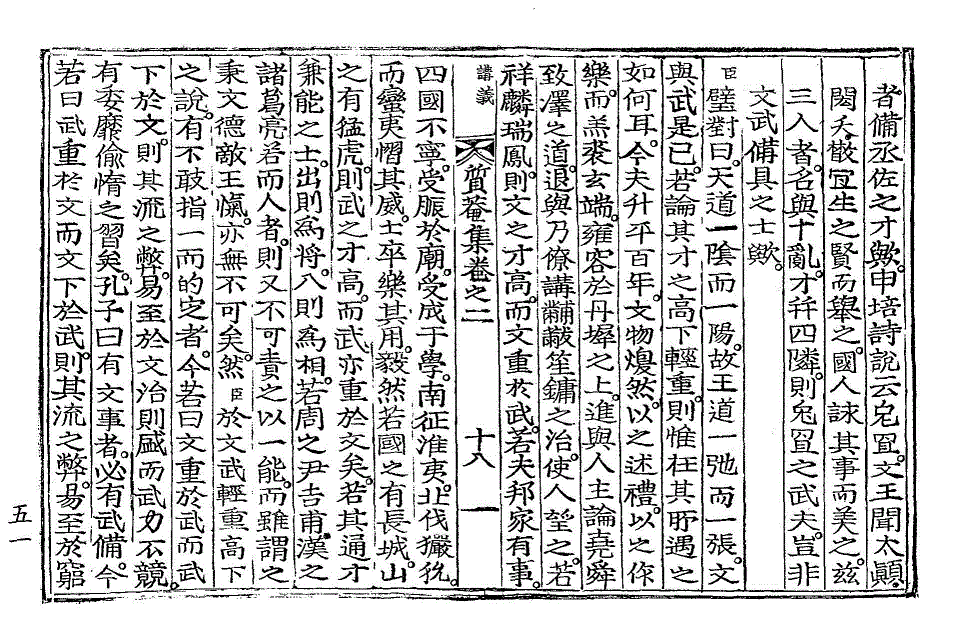 者备丞佐之才欤。申培诗说云兔罝。文王闻太颠,闳夭,散宜生之贤而举之。国人咏其事而美之。玆三人者。名与十乱。才并四邻。则兔罝之武夫。岂非文武备具之士欤。
者备丞佐之才欤。申培诗说云兔罝。文王闻太颠,闳夭,散宜生之贤而举之。国人咏其事而美之。玆三人者。名与十乱。才并四邻。则兔罝之武夫。岂非文武备具之士欤。臣璧对曰。天道一阴而一阳。故王道一弛而一张。文与武是已。若论其才之高下轻种。则惟在其所遇之如何耳。今夫升平百年。文物焕然。以之述礼。以之作乐。而羔裘玄端。雍容于丹墀之上。进与人主论尧舜致凙之道。退与乃僚讲黼黻笙镛之治。使人望之。若祥麟瑞凤。则文之才高。而文重于武。若夫邦家有事。四国不宁。受脤于庙。受成于学。南征淮夷。北伐猃狁。而蛮夷慑其威。士卒乐其用。毅然若国之有长城。山之有猛虎。则武之才高。而武亦重于文矣。若其通才兼能之士。出则为将。入则为相。若周之尹吉甫,汉之诸葛亮若而人者。则又不可责之以一能。而虽谓之秉文德敌王忾。亦无不可矣。然臣于文武轻重高下之说。有不敢指一而的定者。今若曰文重于武而武下于文。则其流之弊。易至于文治则盛而武力不竞。有委靡偷惰之习矣。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若曰武重于文而文下于武。则其流之弊。易至于穷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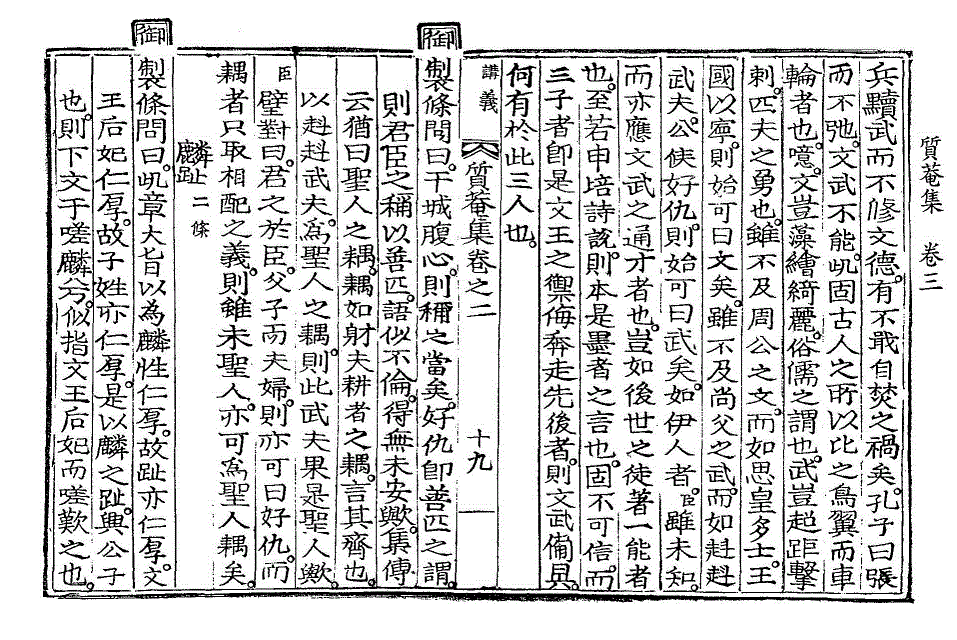 兵黩武而不修文德。有不戢自焚之祸矣。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此固古人之所以比之鸟翼而车轮者也。噫。文岂藻绘绮丽。俗儒之谓也。武岂超距击刺。匹夫之勇也。虽不及周公之文。而如思皇多士。王国以宁。则始可曰文矣。虽不及尚父之武。而如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则始可曰武矣。如伊人者。臣虽未知。而亦应文武之通才者也。岂如后世之徒著一能者也。至若申培诗说。则本是墨者之言也。固不可信。而三子者即是文王之御侮奔走先后者。则文武备具。何有于此三人也。
兵黩武而不修文德。有不戢自焚之祸矣。孔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此固古人之所以比之鸟翼而车轮者也。噫。文岂藻绘绮丽。俗儒之谓也。武岂超距击刺。匹夫之勇也。虽不及周公之文。而如思皇多士。王国以宁。则始可曰文矣。虽不及尚父之武。而如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则始可曰武矣。如伊人者。臣虽未知。而亦应文武之通才者也。岂如后世之徒著一能者也。至若申培诗说。则本是墨者之言也。固不可信。而三子者即是文王之御侮奔走先后者。则文武备具。何有于此三人也。御制条问曰。干城腹心。则称之当矣。好仇即善匹之谓。则君臣之称以善匹。语似不伦。得无未安欤。集传云犹曰圣人之耦。耦如射夫耕者之耦。言其齐也。以赳赳武夫。为圣人之耦。则此武夫果是圣人欤。
臣璧对曰。君之于臣。父子而夫妇。则亦可曰好仇。而耦者只取相配之义。则虽未圣人。亦可为圣人耦矣。
麟趾(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章大旨以为麟性仁厚。故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子姓亦仁厚。是以麟之趾。兴公子也。则下文于嗟麟兮。似指文王后妃而嗟叹之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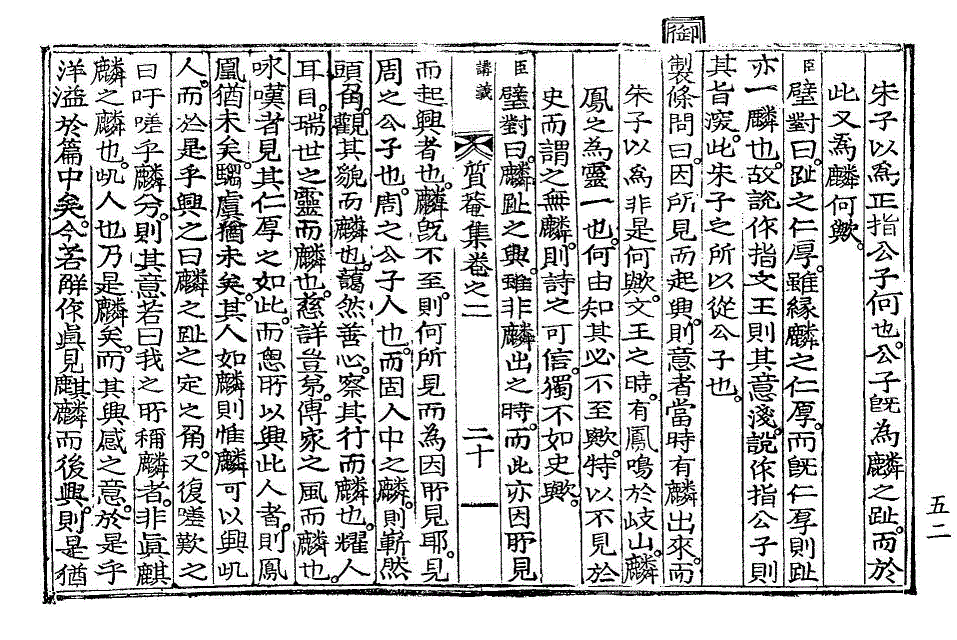 朱子以为正指公子何也。公子既为麟之趾。而于此又为麟何欤。
朱子以为正指公子何也。公子既为麟之趾。而于此又为麟何欤。臣璧对曰。趾之仁厚。虽缘麟之仁厚。而既仁厚则趾亦一麟也。故说作指文王则其意浅。说作指公子则其旨深。此朱子之所以从公子也。
御制条问曰。因所见而起兴。则意者当时有麟出来。而朱子以为非是何欤。文王之时。有凤鸣于岐山。麟凤之为灵一也。何由知其必不至欤。特以不见于史而谓之无麟。则诗之可信。独不如史欤。
臣璧对曰。麟趾之兴。虽非麟出之时。而此亦因所见而起兴者也。麟既不至。则何所见而为因所见耶。见周之公子也。周之公子人也。而固人中之麟。则崭然头角。观其貌而麟也。蔼然善心。察其行而麟也。耀人耳目。瑞世之灵而麟也。慈详岂弟。传家之风而麟也。咏叹者见其仁厚之如此。而思所以兴此人者。则凤凰犹未矣。驺虞犹未矣。其人如麟则惟麟可以兴此人。而于是乎兴之曰麟之趾之定之角。又复嗟叹之曰吁嗟乎麟兮。则其意若曰我之所称麟者。非真麒麟之麟也。此人也乃是麟矣。而其兴感之意。于是乎洋溢于篇中矣。今若解作真见麒麟而后兴。则是犹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3H 页
 属泛忽。而不如朱子之说兴矣。又况世之称周时有麟者。未必非此诗之误解流去而不可取信者耶。
属泛忽。而不如朱子之说兴矣。又况世之称周时有麟者。未必非此诗之误解流去而不可取信者耶。召南
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仪礼乡饮酒乡射礼燕礼。皆合乐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采蘋似是旧在草虫之上矣。移置草虫之下者。果自何氏始欤。
臣璧对曰。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小雅之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有台。莫不以上三篇次第为歌。则采蘋之必先于草虫。固已明矣。臣虽未的知移置之昉自何人。而窃想其移置之意。不过欲以召南作周南之对待。故以鹊巢应关雎。以采蘩为公桑而以应葛覃。采蘋不可与卷耳相应。故移置草虫于上以应之。是只知周召南之为相应。而不知乐歌之有次序。不可以间越也。考诸小序。已以采蘋下于草虫。则是必作小序者移置之。而不然则是毛公分配小序时事也。
鹊巢(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章只取鸠性之拙。以比妇德之专静。似非有他义。而或谓以他国之子而来享此国之成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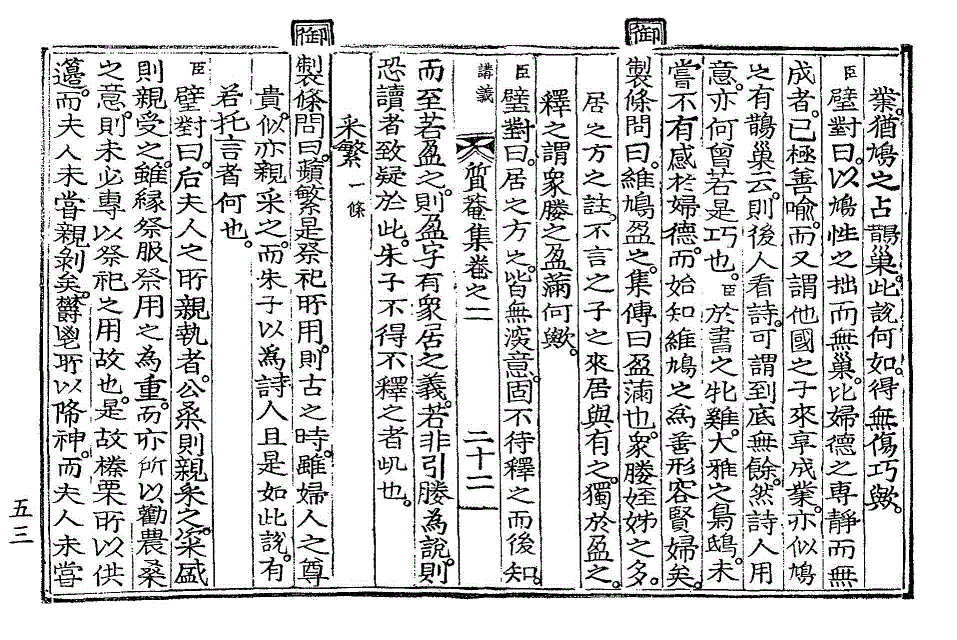 业。犹鸠之占鹊巢。此说何如。得无伤巧欤。
业。犹鸠之占鹊巢。此说何如。得无伤巧欤。臣璧对曰。以鸠性之拙而无巢。比妇德之专静而无成者。已极善喻。而又谓他国之子来享成业。亦似鸠之有鹊巢云。则后人看诗。可谓到底无馀。然诗人用意。亦何曾若是巧也。臣于书之牝鸡。大雅之枭鸱。未尝不有感于妇德。而始知维鸠之为善形容贤妇矣。
御制条问曰。维鸠盈之。集传曰盈满也。众媵侄姊之多。居之方之注。不言之子之来居与有之。独于盈之。释之谓众媵之盈满何欤。
臣璧对曰。居之方之。皆无深意。固不待释之而后知。而至若盈之。则盈字有众居之义。若非引媵为说。则恐读者致疑于此。朱子不得不释之者此也。
采繁(一条)
御制条问曰。蘋繁是祭祀所用。则古之时。虽妇人之尊贵。似亦亲采之。而朱子以为诗人且是如此说。有若托言者何也。
臣璧对曰。后夫人之所亲执者。公桑则亲采之。粢盛则亲受之。虽缘祭服祭用之为重。而亦所以劝农桑之意。则未必专以祭祀之用故也。是故榛栗所以供笾。而夫人未尝亲剥矣。郁鬯所以降神。而夫人未尝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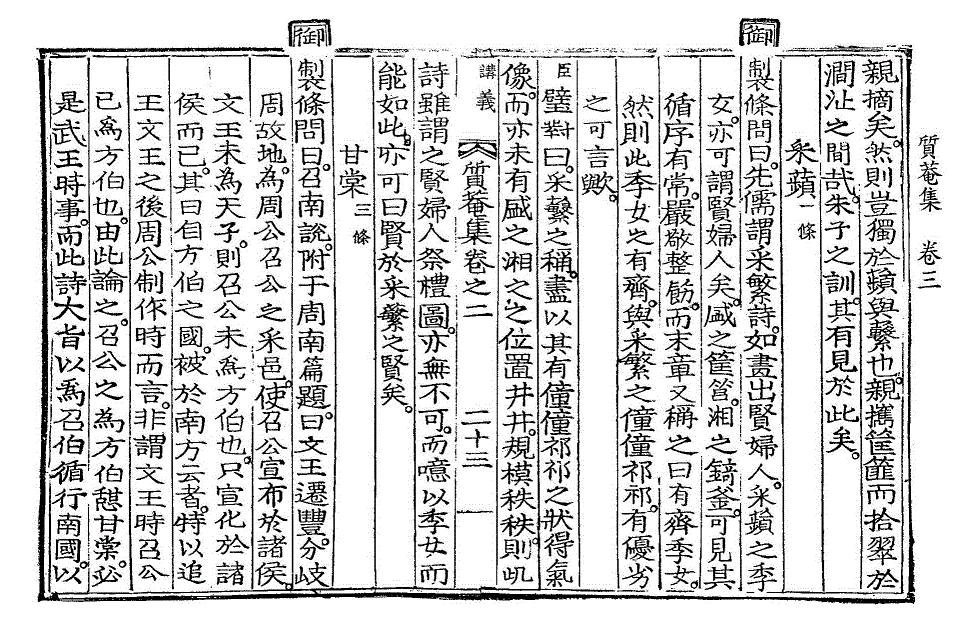 亲摘矣。然则岂独于蘋与系也。亲携筐篚而拾翠于涧沚之间哉。朱子之训。其有见于此矣。
亲摘矣。然则岂独于蘋与系也。亲携筐篚而拾翠于涧沚之间哉。朱子之训。其有见于此矣。采蘋(一条)
御制条问曰。先儒谓采繁诗。如画出贤妇人。采蘋之季女。亦可谓贤妇人矣。盛之筐筥。湘之锜釜。可见其循序有常。严敬整饬。而末章又称之曰有齐季女。然则此季女之有齐。与采繁之僮僮祁祁。有优劣之可言欤。
臣璧对曰。采蘩之称。尽以其有僮僮祁祁之状得气像。而亦未有盛之湘之之位置井井。规模秩秩。则此诗虽谓之贤妇人祭礼图。亦无不可。而噫以季女而能如此。亦可曰贤于采蘩之贤矣。
甘棠(三条)
御制条问曰。召南说。附于周南篇题。曰文王迁丰。分岐周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召公宣布于诸侯。文王未为天子。则召公未为方伯也。只宣化于诸侯而已。其曰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云者。特以追王文王之后周公制作时而言。非谓文王时召公已为方伯也。由此论之。召公之为方伯憩甘棠。必是武王时事。而此诗大旨以为召伯循行南国。以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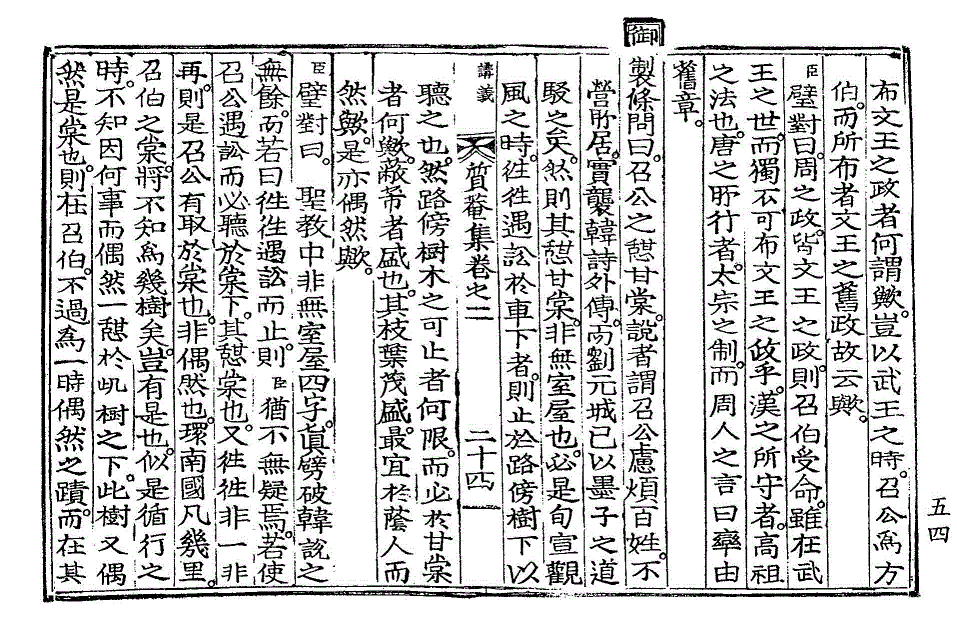 布文王之政者何谓欤。岂以武王之时。召公为方伯。而所布者文王之旧政故云欤。
布文王之政者何谓欤。岂以武王之时。召公为方伯。而所布者文王之旧政故云欤。臣璧对曰。周之政。皆文王之政。则召伯受命。虽在武王之世。而独不可布文王之政乎。汉之所守者。高祖之法也。唐之所行者。太宗之制。而周人之言曰率由旧章。
御制条问曰。召公之憩甘棠。说者谓召公虑烦百姓。不营所居。实袭韩诗外传。而刘元城已以墨子之道驳之矣。然则其憩甘棠。非无室屋也。必是旬宣观风之时。往往遇讼于车下者。则止于路傍树下以听之也。然路傍树木之可止者何限。而必于甘棠者何欤。蔽芾者盛也。其枝叶茂盛。最宜于荫人而然欤。是亦偶然欤。
臣璧对曰。 圣教中非无室屋四字。真劈破韩说之无馀。而若曰往往遇讼而止。则臣犹不无疑焉。若使召公遇讼而必听于棠下。其憩棠也。又往往非一非再。则是召公有取于棠也。非偶然也。环南国凡几里。召伯之棠。将不知为几树矣。岂有是也。似是循行之时。不知因何事而偶然一憩于此树之下。此树又偶然是棠也。则在召伯。不过为一时偶然之迹。而在其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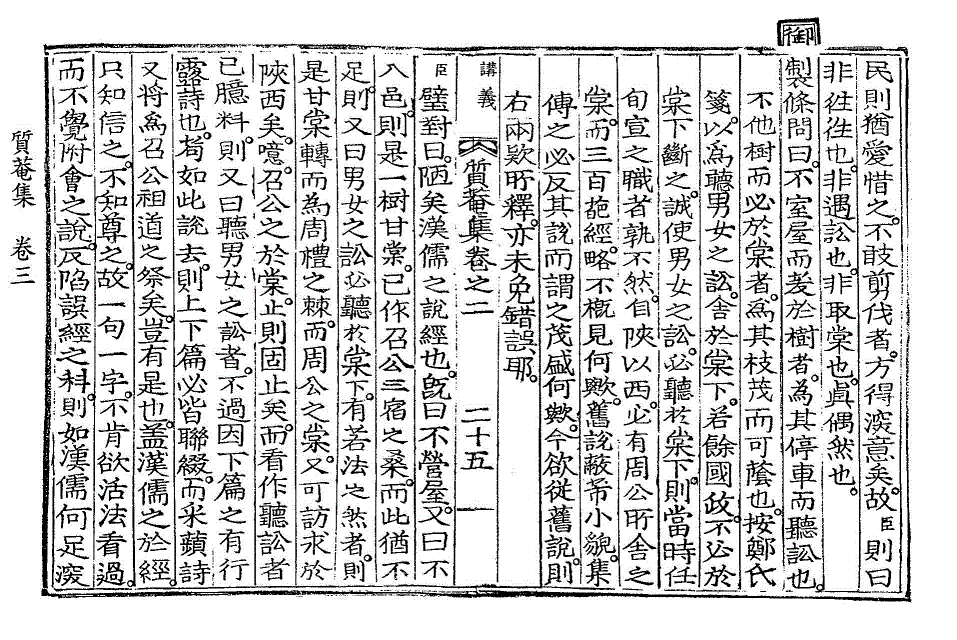 民则犹爱惜之。不敢剪伐者。方得深意矣。故臣则曰非往往也。非遇讼也。非取棠也。真偶然也。
民则犹爱惜之。不敢剪伐者。方得深意矣。故臣则曰非往往也。非遇讼也。非取棠也。真偶然也。御制条问曰。不室屋而茇于树者。为其停车而听讼也。不他树而必于棠者。为其枝茂而可荫也。按郑氏笺。以为听男女之讼。舍于棠下。若馀国政。不必于棠下断之。诚使男女之讼。必听于棠下。则当时任旬宣之职者孰不然。自陕以西。必有周公所舍之棠。而三百葩经。略不概见何欤。旧说蔽芾小貌。集传之必反其说而谓之茂盛何欤。今欲从旧说。则右两款所释。亦未免错误耶。
臣璧对曰。陋矣汉儒之说经也。既曰不营屋。又曰不入邑。则是一树甘棠。已作召公三宿之桑。而此犹不足。则又曰男女之讼必听于棠下。有若法之然者。则是甘棠转而为周礼之棘。而周公之棠。又可访求于陕西矣。噫。召公之于棠。止则固止矣。而看作听讼者已臆料。则又曰听男女之讼者。不过因下篇之有行露诗也。苟如此说去。则上下篇必皆联缀。而采蘋诗又将为召公祖道之祭矣。岂有是也。盖汉儒之于经。只知信之。不知尊之。故一句一字。不肯欲活法看过。而不觉附会之说。反陷误经之科。则如汉儒何足深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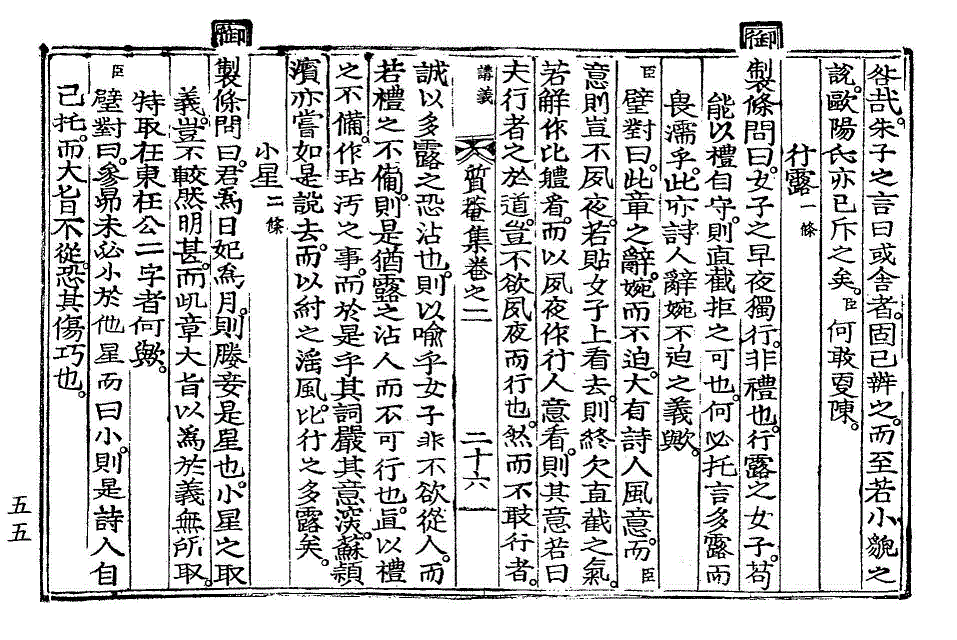 咎哉。朱子之言曰或舍者。固已辨之。而至若小貌之说。欧阳氏亦已斥之矣。臣何敢更陈。
咎哉。朱子之言曰或舍者。固已辨之。而至若小貌之说。欧阳氏亦已斥之矣。臣何敢更陈。行露(一条)
御制条问曰。女子之早夜独行。非礼也。行露之女子。苟能以礼自守。则直截拒之可也。何必托言多露而畏濡乎。此亦诗人辞婉不迫之义欤。
臣璧对曰。此章之辞。婉而不迫。大有诗人风意。而臣意则岂不夙夜。若贴女子上看去。则终欠直截之气。若解作比体看。而以夙夜作行人意看。则其意若曰夫行者之于道。岂不欲夙夜而行也。然而不敢行者。诚以多露之恐沾也。则以喻乎女子非不欲从人。而若礼之不备。则是犹露之沾人而不可行也。直以礼之不备。作玷污之事。而于是乎其词严其意深。苏颖滨亦尝如是说去。而以纣之淫风。比行之多露矣。
小星(二条)
御制条问曰。君为日妃为月。则媵妾是星也。小星之取义。岂不较然明甚。而此章大旨以为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二字者何欤。
臣璧对曰。参昴未必小于他星而曰小。则是诗人自己托。而大旨不从。恐其伤巧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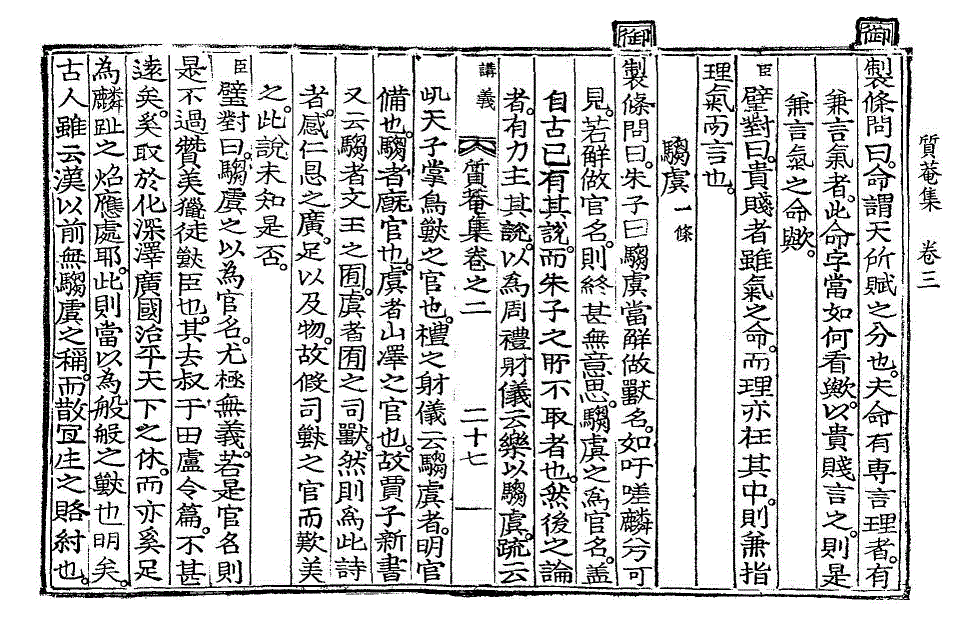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命谓天所赋之分也。夫命有专言理者。有兼言气者。此命字当如何看欤。以贵贱言之。则是兼言气之命欤。
御制条问曰。命谓天所赋之分也。夫命有专言理者。有兼言气者。此命字当如何看欤。以贵贱言之。则是兼言气之命欤。臣璧对曰。贵贱者虽气之命。而理亦在其中。则兼指理气而言也。
驺虞(一条)
御制条问曰。朱子曰驺虞当解做兽名。如吁嗟麟兮可见。若解做官名。则终甚无意思。驺虞之为官名。盖自古已有其说。而朱子之所不取者也。然后之论者。有力主其说。以为周礼射仪云乐以驺虞。疏云此天子掌鸟兽之官也。礼之射仪云驺虞者。明官备也。驺者厩官也。虞者山凙之官也。故贾子新书又云驺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兽。然则为此诗者。感仁恩之广。足以及物。故假司兽之官而叹美之。此说未知是否。
臣璧对曰。驺虞之以为官名。尤极无义。若是官名则是不过赞美猎徒兽臣也。其去叔于田卢令篇。不甚远矣。奚取于化深泽广国治平天下之休。而亦奚足为麟趾之炤应处耶。此则当以为般般之兽也明矣。古人虽云汉以前无驺虞之称。而散宜生之赂纣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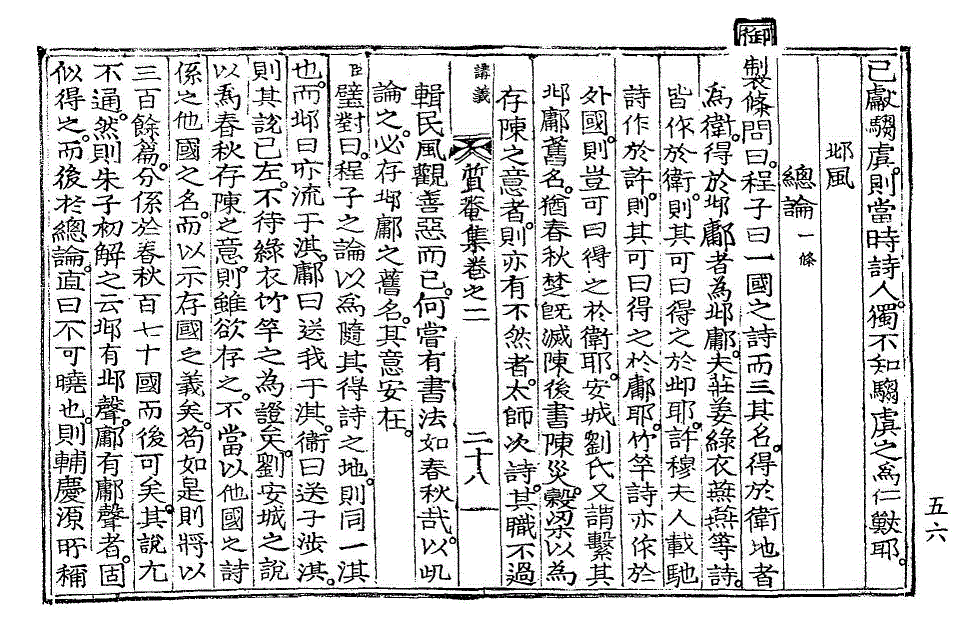 已献驺虞。则当时诗人。独不如驺虞之为仁兽耶。
已献驺虞。则当时诗人。独不如驺虞之为仁兽耶。邶风
总论(一条)
御制条问曰。程子曰一国之诗而三其名。得于卫地者为卫。得于邶鄘者为邶鄘。夫庄姜绿衣燕燕等诗。皆作于卫。则其可曰得之于邶耶。许穆夫人载驰诗作于许。则其可曰得之于鄘耶。竹竿诗亦作于外国。则岂可曰得之于卫耶。安城刘氏又谓系其邶鄘旧名。犹春秋楚既灭陈后书陈灾。谷梁以为存陈之意者。则亦有不然者。太师次诗。其职不过辑民风观善恶而已。何尝有书法如春秋哉。以此论之。必存邶鄘之旧名。其意安在。
臣璧对曰。程子之论以为随其得诗之地。则同一淇也。而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于淇。卫曰送子涉淇。则其说已左。不待绿衣竹竿之为證矣。刘安城之说以为春秋存陈之意。则虽欲存之。不当以他国之诗系之他国之名。而以示存国之义矣。苟如是则将以三百馀篇。分系于春秋百七十国而后可矣。其说尤不通。然则朱子初解之云邶有邶声。鄘有鄘声者。固似得之。而后于总论。直曰不可晓也。则辅庆源所称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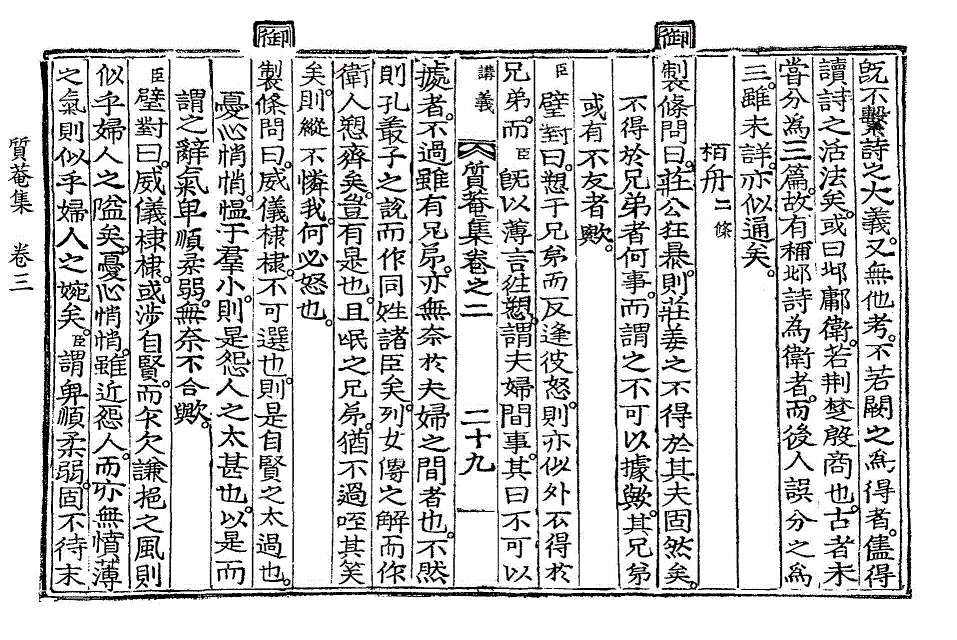 既不系诗之大义。又无他考。不若阙之为得者。尽得读诗之活法矣。或曰邶鄘卫。若荆楚殷商也。古者未尝分为三篇。故有称邶诗为卫者。而后人误分之为三。虽未详。亦似通矣。
既不系诗之大义。又无他考。不若阙之为得者。尽得读诗之活法矣。或曰邶鄘卫。若荆楚殷商也。古者未尝分为三篇。故有称邶诗为卫者。而后人误分之为三。虽未详。亦似通矣。柏舟(二条)
御制条问曰。庄公狂暴。则庄姜之不得于其夫固然矣。不得于兄弟者何事。而谓之不可以据欤。其兄弟或有不友者欤。
臣璧对曰。愬于兄弟而反逢彼怒。则亦似外不得于兄弟。而臣既以薄言往愬。谓夫妇间事。其曰不可以据者。不过虽有兄弟。亦无奈于夫妇之间者也。不然则孔丛子之说而作同姓诸臣矣。列女传之解而作卫人愬齐矣。岂有是也。且氓之兄弟。犹不过咥其笑矣。则纵不怜我。何必怒也。
御制条问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则是自贤之太过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则是怨人之太甚也。以是而谓之辞气卑顺柔弱。无奈不合欤。
臣璧对曰。威仪棣棣。或涉自贤。而乍欠谦挹之风则似乎妇人之隘矣。忧心悄悄。虽近怨人。而亦无愤薄之气则似乎妇人之婉矣。臣谓卑顺柔弱。固不待末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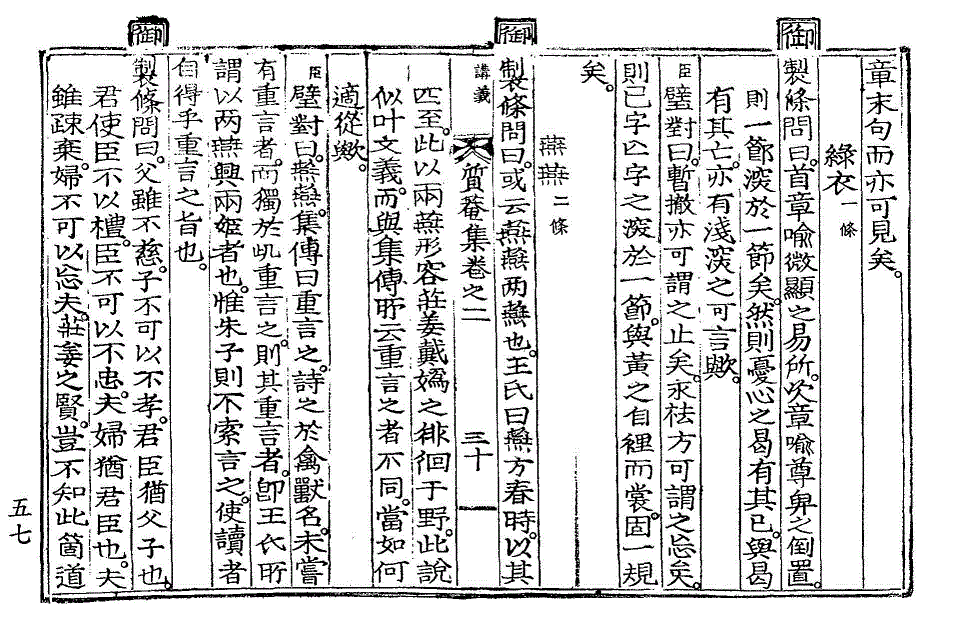 章末句而亦可见矣。
章末句而亦可见矣。绿衣(一条)
御制条问曰。首章喻微显之易所。次章喻尊卑之倒置。则一节深于一节矣。然则忧心之曷有其已。与曷有其亡。亦有浅深之可言欤。
臣璧对曰。暂撤亦可谓之止矣。永祛方可谓之忘矣。则已字亡字之深于一节。与黄之自里而裳。固一规矣。
燕燕(二条)
御制条问曰。或云燕燕两燕也。王氏曰燕方春时。以其匹至。此以两燕形容庄姜戴妫之徘徊于野。此说似叶文义。而与集传所云重言之者不同。当如何适从欤。
臣璧对曰。燕燕。集传曰重言之。诗之于禽兽名。未尝有重言者。而独于此重言之。则其重言者。即王氏所谓以两燕兴两姬者也。惟朱子则不索言之。使读者自得乎重言之旨也。
御制条问曰。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臣犹父子也。君使臣不以礼。臣不可以不忠。夫妇犹君臣也。夫虽疏弃。妇不可以忘夫。庄姜之贤。岂不知此个道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8H 页
 理乎。且凡人于先君。忠心易衰。则易致日远而月忘。甚则或有以为无能而倍之者矣。庄姜之贤。又岂有是乎。然而戴妫必以先君之思勖勉庄姜。若虑夫庄姜之不足于此何也。且送人。赠之以言礼也。戴妫之留别庄姜。勖之以思先君。而庄姜之于戴妫。只一味赞叹其德美。而无一言劝勉何欤。
理乎。且凡人于先君。忠心易衰。则易致日远而月忘。甚则或有以为无能而倍之者矣。庄姜之贤。又岂有是乎。然而戴妫必以先君之思勖勉庄姜。若虑夫庄姜之不足于此何也。且送人。赠之以言礼也。戴妫之留别庄姜。勖之以思先君。而庄姜之于戴妫。只一味赞叹其德美。而无一言劝勉何欤。臣璧对曰。先君之思者。虽曰戴妫之勉。而即是庄姜之诗。则使庄姜果不足于此而戴妫勉之欤。庄姜未必以其言为贤而著之于篇。于此可见庄姜之所以雨泣劳心者。莫非思先君以及于妫也。且终字有将来冀望之意。其曰温惠淑慎。未必徒归于赞叹矣。其赞其固有以勉行者。道其所告以自勉旃者。亦庄姜赠言之意也。
日月(一条)
御制条问曰。日居月诸。呼而诉之也。不呼旻天而呼日月者何也。日月即天之精光也。呼日月则便是呼天欤。照临下土与下土是冒。即言仰冀两耀无私之照。俯烛一妇见弃之冤。固有其义。而至于出自东方之云。则似无意思。果何谓欤。
臣璧对曰。天之所以照物者日月也。则呼日月而冀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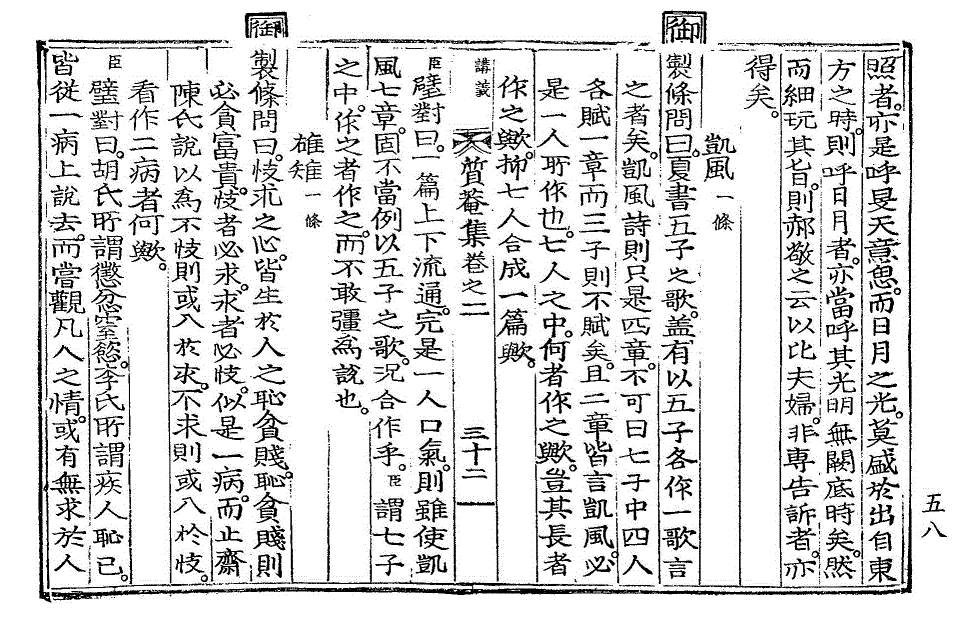 照者。亦是呼旻天意思。而日月之光。莫盛于出自东方之时。则呼日月者。亦当呼其光明无阙底时矣。然而细玩其旨。则郝敬之云以比夫妇。非专告诉者。亦得矣。
照者。亦是呼旻天意思。而日月之光。莫盛于出自东方之时。则呼日月者。亦当呼其光明无阙底时矣。然而细玩其旨。则郝敬之云以比夫妇。非专告诉者。亦得矣。凯风(一条)
御制条问曰。夏书五子之歌。盖有以五子各作一歌言之者矣。凯风诗则只是四章。不可曰七子中四人各赋一章而三子则不赋矣。且二章皆言凯风。必是一人所作也。七人之中。何者作之欤。岂其长者作之欤。抑七人合成一篇欤。
臣璧对曰。一篇上下流通。完是一人口气。则虽使凯风七章。固不当例以五子之歌。况合作乎。臣谓七子之中。作之者作之。而不敢彊为说也。
雄雉(一条)
御制条问曰。忮求之心。皆生于人之耻贫贱。耻贫贱则必贪富贵。忮者必求。求者必忮。似是一病。而止斋陈氏说以为不忮则或入于求。不求则或入于忮。看作二病者何欤。
臣璧对曰。胡氏所谓惩忿窒欲。李氏所谓疾人耻己。皆从一病上说去。而尝观凡人之情。或有无求于人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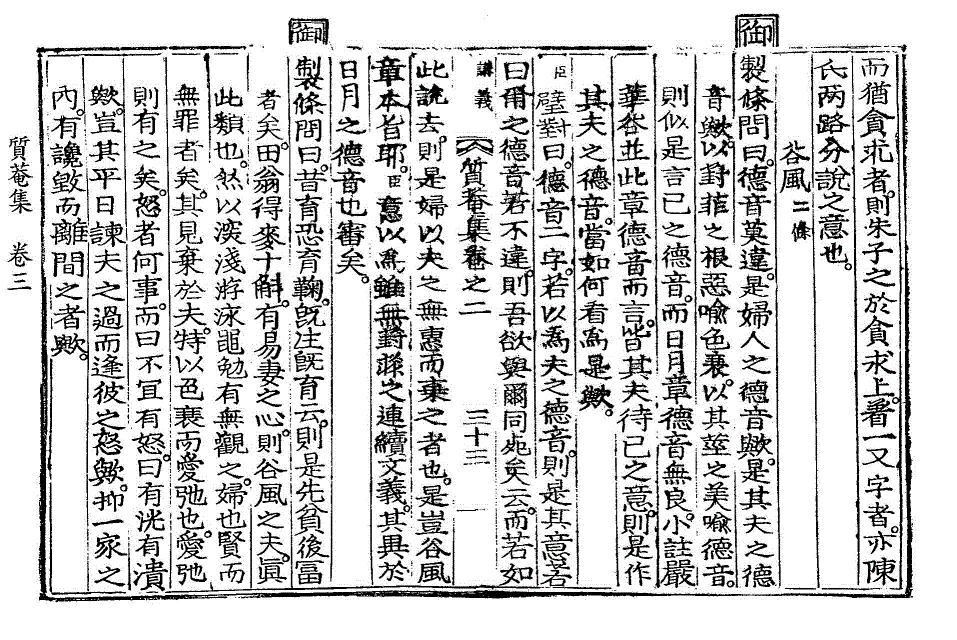 而犹贪求者。则朱子之于贪求上。着一又字者。亦陈氏两路分说之意也。
而犹贪求者。则朱子之于贪求上。着一又字者。亦陈氏两路分说之意也。谷风(二条)
御制条问曰。德音莫违。是妇人之德音欤。是其夫之德音欤。以葑菲之根恶喻色衰。以其茎之美喻德音。则似是言己之德音。而日月章德音无良。小注严华谷并此章德音而言。皆其夫待己之意。则是作其夫之德音。当如何看为是欤。
臣璧对曰。德音二字。若以为夫之德音。则是其意若曰尔之德音若不违。则吾欲与尔同死矣云。而若如此说去。则是妇以夫之无惠而弃之者也。是岂谷风章本旨耶。臣意以为虽无葑菲之连续文义。其异于日月之德音也审矣。
御制条问曰。昔育恐育鞠。既生既育云。则是先贫后富者矣。田翁得麦十斛。有易妻之心。则谷风之夫。真此类也。然以深浅游泳黾勉有无观之。妇也贤而无罪者矣。其见弃于夫。特以色衰而爱弛也。爱弛则有之矣。怒者何事。而曰不宜有怒。曰有洸有溃欤。岂其平日谏夫之过而逢彼之怒欤。抑一家之内。有谗毁而离间之者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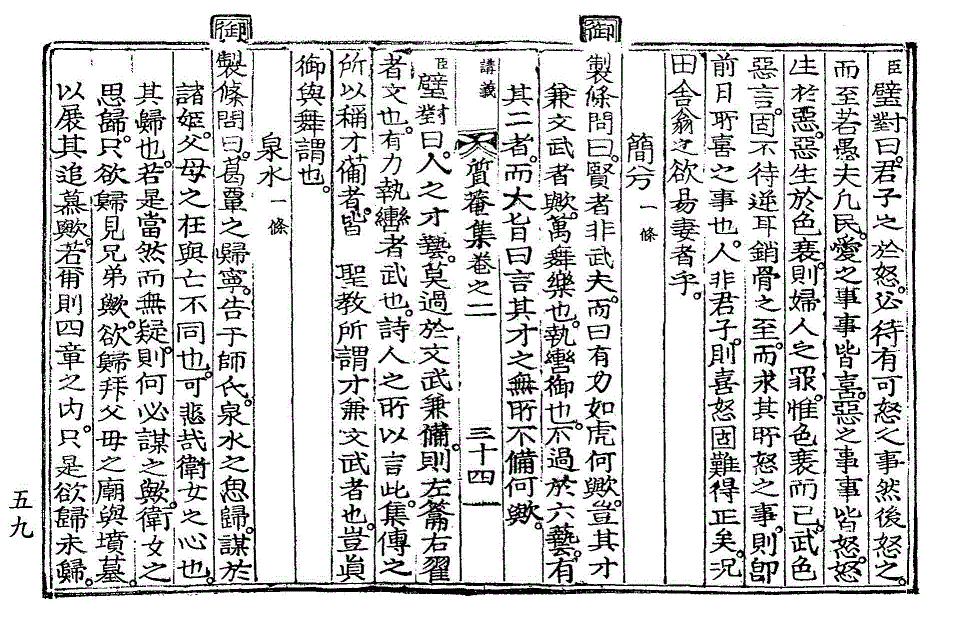 臣璧对曰。君子之于怒。必待有可怒之事然后怒之。而至若愚夫凡民。爱之事事皆喜。恶之事事皆怒。怒生于恶。恶生于色衰。则妇人之罪。惟色衰而已。武色恶言。固不待逆耳销骨之至。而求其所怒之事。则即前日所喜之事也。人非君子。则喜怒固难得正矣。况田舍翁之欲易妻者乎。
臣璧对曰。君子之于怒。必待有可怒之事然后怒之。而至若愚夫凡民。爱之事事皆喜。恶之事事皆怒。怒生于恶。恶生于色衰。则妇人之罪。惟色衰而已。武色恶言。固不待逆耳销骨之至。而求其所怒之事。则即前日所喜之事也。人非君子。则喜怒固难得正矣。况田舍翁之欲易妻者乎。简兮(一条)
御制条问曰。贤者非武夫。而曰有力如虎何欤。岂其才兼文武者欤。万舞乐也。执辔御也。不过于六艺。有其二者。而大旨曰言其才之无所不备何欤。
臣璧对曰。人之才艺。莫过于文武兼备。则左籥右翟者文也。有力执辔者武也。诗人之所以言此。集传之所以称才备者。皆 圣教所谓才兼文武者也。岂真御与舞谓也。
泉水(一条)
御制条问曰。葛覃之归宁。告于师氏。泉水之思归。谋于诸姬。父母之在与亡不同也。可悲哉卫女之心也。其归也。若是当然而无疑。则何必谋之欤。卫女之思归。只欲归见兄弟欤。欲归拜父母之庙与坟墓。以展其追慕欤。若尔则四章之内。只是欲归未归。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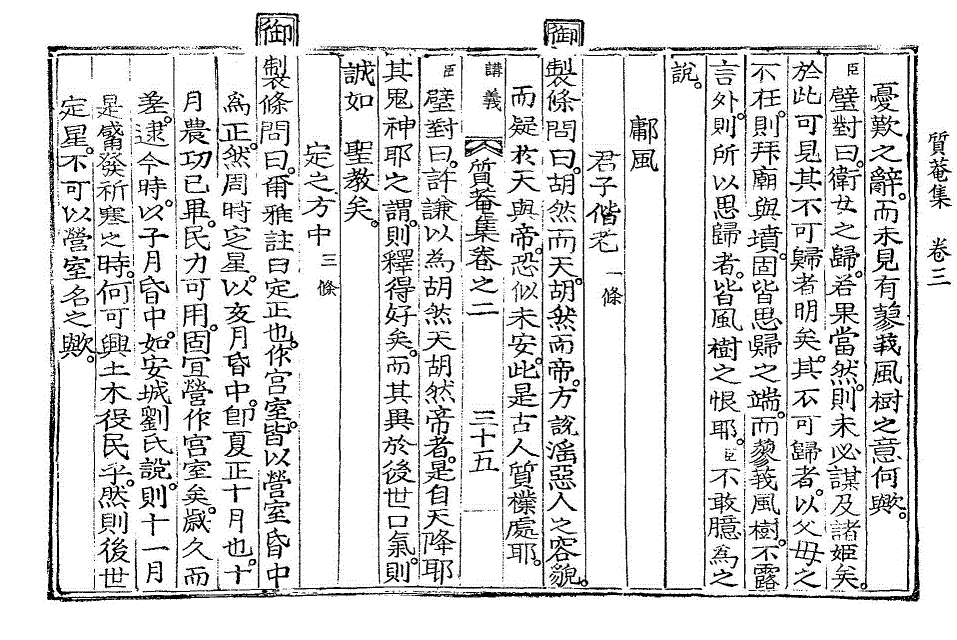 忧叹之辞。而未见有蓼莪风树之意何欤。
忧叹之辞。而未见有蓼莪风树之意何欤。臣璧对曰。卫女之归。若果当然。则未必谋及诸姬矣。于此可见其不可归者明矣。其不可归者。以父母之不在。则拜庙与坟。固皆思归之端。而蓼莪风树。不露言外。则所以思归者。皆风树之恨耶。臣不敢臆为之说。
鄘风
君子偕老(一条)
御制条问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方说淫恶人之容貌。而疑于天与帝。恐似未安。此是古人质朴处耶。
臣璧对曰。许谦以为胡然天胡然帝者。是自天降耶其鬼神耶之谓。则释得好矣。而其异于后世口气。则诚如 圣教矣。
定之方中(三条)
御制条问曰。尔雅注曰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昏中为正。然周时定星。以亥月昏中。即夏正十月也。十月农功已毕。民力可用。固宜营作宫室矣。岁久而差。逮今时。以子月昏中。如安城刘氏说。则十一月是觱发祈寒之时。何可兴土木役民乎。然则后世定星。不可以营室名之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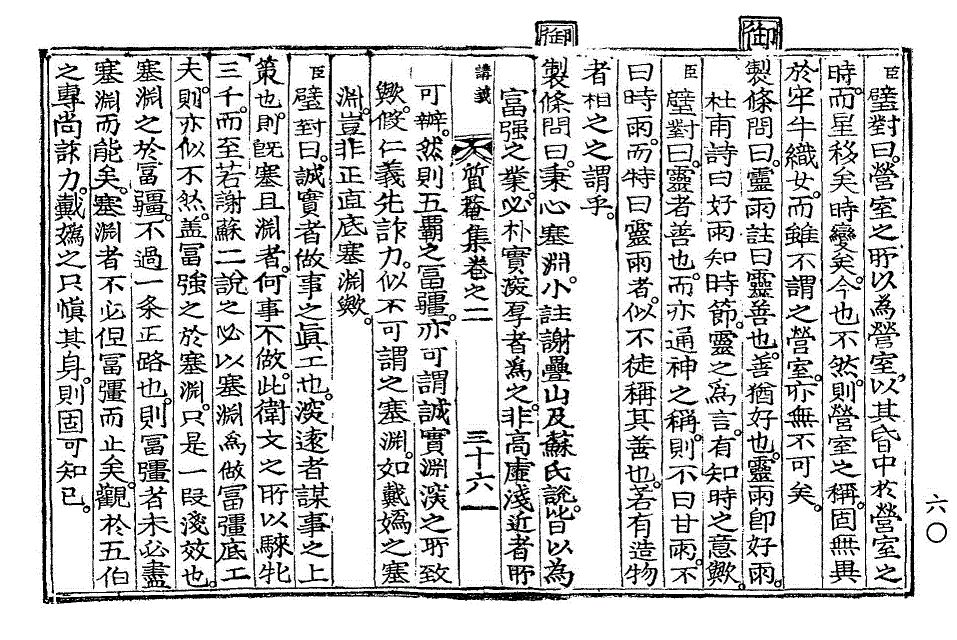 臣璧对曰。营室之所以为营室。以其昏中于营室之时。而星移矣时变矣。今也不然。则营室之称。固无异于牢(一作牵)牛织女。而虽不谓之营室。亦无不可矣。
臣璧对曰。营室之所以为营室。以其昏中于营室之时。而星移矣时变矣。今也不然。则营室之称。固无异于牢(一作牵)牛织女。而虽不谓之营室。亦无不可矣。御制条问曰。灵雨注曰灵善也。善犹好也。灵雨即好雨。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灵之为言。有知时之意欤。
臣璧对曰。灵者善也。而亦通神之称。则不曰甘雨。不曰时雨。而特曰灵雨者。似不徒称其善也。若有造物者相之之谓乎。
御制条问曰。秉心塞渊。小注谢叠山及苏氏说。皆以为富强之业。必朴实深厚者为之。非高虚浅近者所可办。然则五霸之富疆。亦可谓诚实渊深之所致欤。假仁义先诈力。似不可谓之塞渊。如戴妫之塞渊。岂非正直底塞渊欤。
臣璧对曰。诚实者做事之真工也。深远者谋事之上策也。则既塞且渊者。何事不做。此卫文之所以騋牝三千。而至若谢苏二说之必以塞渊为做富彊底工夫。则亦似不然。盖富强之于塞渊。只是一段浅效也。塞渊之于富疆。不过一条正路也。则富彊者未必尽塞渊而能矣。塞渊者不必但富彊而止矣。观于五伯之专尚诈力。戴妫之只慎其身。则固可知已。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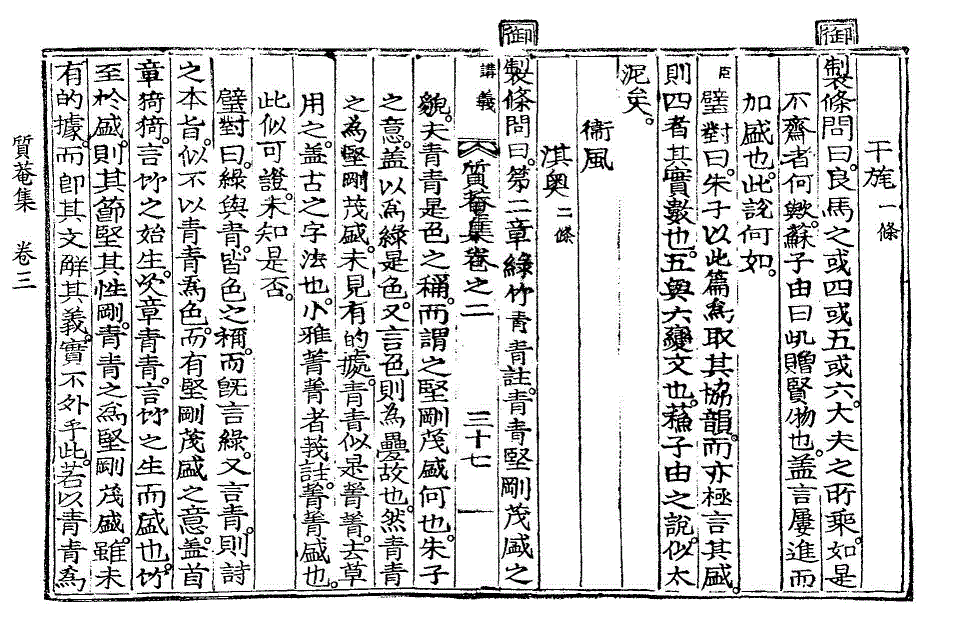 干旄(一条)
干旄(一条)御制条问曰。良马之或四或五或六。大夫之所乘。如是不斋者何欤。苏子由曰此赠贤物也。盖言屡进而加盛也。此说何如。
臣璧对曰。朱子以此篇为取其协韵。而亦极言其盛。则四者其实数也。五与六变文也。苏子由之说。似太泥矣。
卫风
淇奥(二条)
御制条问曰。第二章绿竹青青注。青青坚刚茂盛之貌。夫青青是色之称。而谓之坚刚茂盛何也。朱子之意。盖以为绿是色。又言色则为叠故也。然青青之为坚刚茂盛。未见有的据。青青似是菁菁。去草用之。盖古之字法也。小雅菁菁者莪注。菁菁盛也。此似可證。未知是否。
璧对曰。绿与青。皆色之称。而既言绿。又言青。则诗之本旨。似不以青青为色。而有坚刚茂盛之意。盖首章猗猗。言竹之始生。次章青青。言竹之生而盛也。竹至于盛。则其节坚其性刚。青青之为坚刚茂盛。虽未有的据。而即其文解其义。实不外乎此。若以青青为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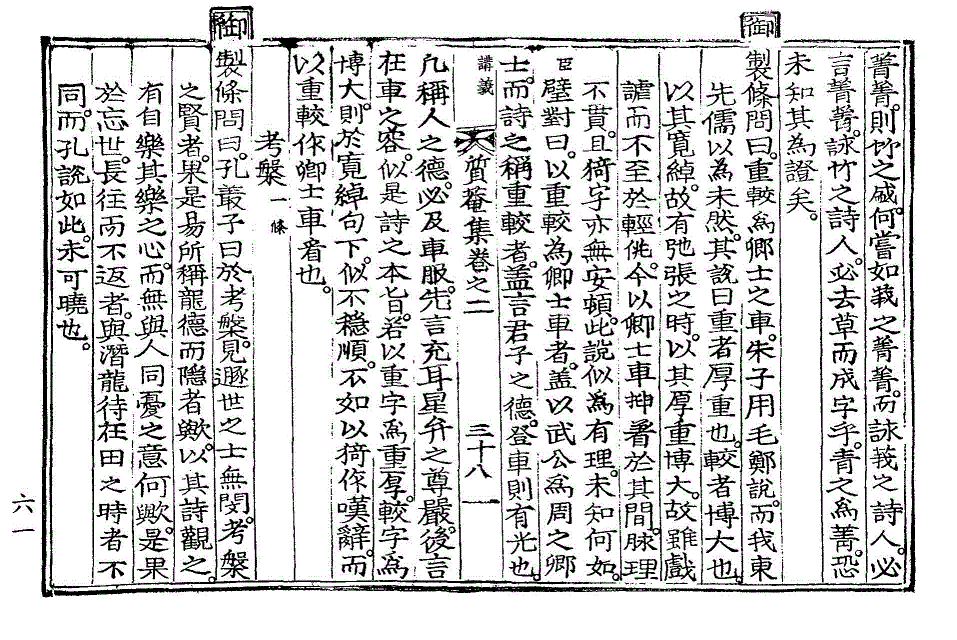 菁菁。则竹之盛。何尝如莪之菁菁。而咏莪之诗人。必言菁菁。咏竹之诗人。必去草而成字乎。青之为菁。恐未知其为證矣。
菁菁。则竹之盛。何尝如莪之菁菁。而咏莪之诗人。必言菁菁。咏竹之诗人。必去草而成字乎。青之为菁。恐未知其为證矣。御制条问曰。重较为卿士之车。朱子用毛郑说。而我东先儒以为未然。其说曰重者厚重也。较者博大也。以其宽绰。故有弛张之时。以其厚重博大。故虽戏谑而不至于轻佻。今以卿士车插着于其间。脉理不贯。且猗字亦无安顿。此说似为有理。未知何如。
臣璧对曰。以重较为卿士车者。盖以武公为周之卿士。而诗之称重较者。盖言君子之德。登车则有光也。凡称人之德。必及车服。先言充耳星弁之尊严。后言在车之容。似是诗之本旨。若以重字为重厚。较字为博大。则于宽绰句下。似不稳顺。不如以猗作叹辞。而以重较作卿士车看也。
考槃(一条)
御制条问曰。孔丛子曰于考槃。见遁世之士无闵。考槃之贤者。果是易所称龙德而隐者欤。以其诗观之。有自乐其乐之心。而无与人同忧之意何欤。是果于忘世。长往而不返者。与潜龙待在田之时者不同。而孔说如此。未可晓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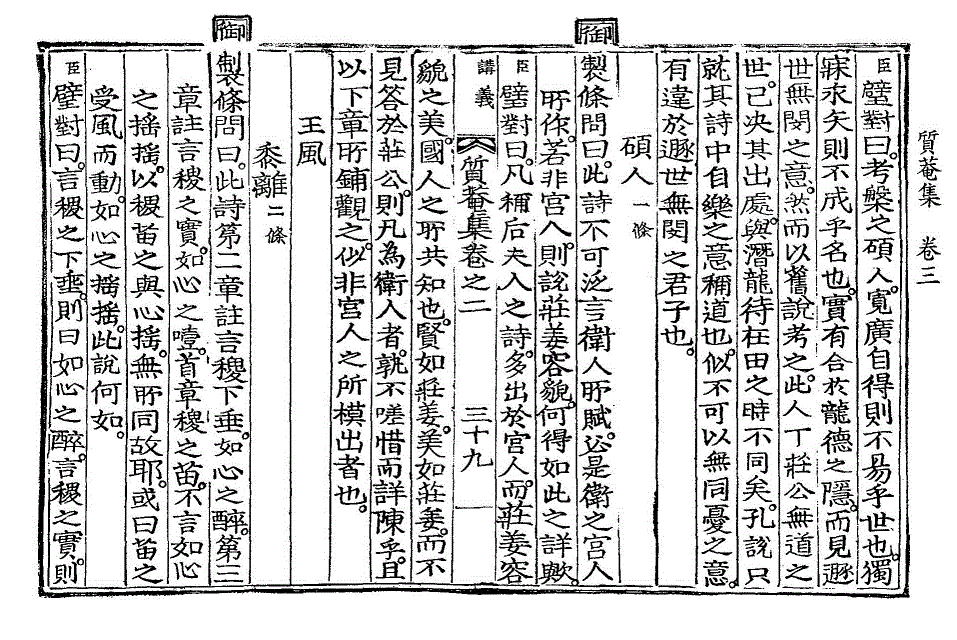 臣璧对曰。考槃之硕人。宽广自得则不易乎世也。独寐永矢则不成乎名也。实有合于龙德之隐。而见遁世无闵之意。然而以旧说考之。此人丁庄公无道之世。已决其出处。与潜龙待在田之时不同矣。孔说只就其诗中自乐之意称道也。似不可以无同忧之意。有违于遁世无闵之君子也。
臣璧对曰。考槃之硕人。宽广自得则不易乎世也。独寐永矢则不成乎名也。实有合于龙德之隐。而见遁世无闵之意。然而以旧说考之。此人丁庄公无道之世。已决其出处。与潜龙待在田之时不同矣。孔说只就其诗中自乐之意称道也。似不可以无同忧之意。有违于遁世无闵之君子也。硕人(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不可泛言卫人所赋。必是卫之宫人所作。若非宫人。则说庄姜容貌。何得如此之详欤。
臣璧对曰。凡称后夫人之诗。多出于宫人。而庄姜容貌之美。国人之所共知也。贤如庄姜。美如庄姜。而不见答于庄公。则凡为卫人者。孰不嗟惜而详陈乎。且以下章所铺观之。似非宫人之所模出者也。
王风
黍离(二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第二章注言稷下垂。如心之醉。第三章注言稷之实。如心之噎。首章稷之苗。不言如心之摇摇。以稷苗之与心摇。无所同故耶。或曰苗之受风而动。如心之摇摇。此说何如。
臣璧对曰。言稷之下垂。则曰如心之醉。言稷之实。则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2L 页
 曰如心之噎。这里两如字。似亦可疑。而然而观大旨辞意。则取兴之义自在其中。或者受风摇摇之说。恐涉于疆把捉也。
曰如心之噎。这里两如字。似亦可疑。而然而观大旨辞意。则取兴之义自在其中。或者受风摇摇之说。恐涉于疆把捉也。御制条问曰。刘元城曰行役往来。固非一见。然则此诗之作。在于三见之后。方见稷之实。而追叙见苗见穗。并以起咏欤。
臣璧对曰。既见苗而又见穗。既见穗而又见实。则再见之感。深于一见。三见之感。深于再见。而及至见实之时。追叙其见苗见穗之事。元城之说。深得风人之旨也。
君子于役(一条)
御制条问曰。羊牛下来注曰羊先归而牛次之。然则下章先言牛何欤。
臣璧对曰。晚出早归。羊之性也。则上章之言羊先于牛者。固其宜矣。而下章之错言者。恐以为诗之变文也。旧说则皆称羊牛。似是明證矣。
扬之水(一条)
御制条问曰。扬水似是言王室之微弱。如水之柔弱。以此意看则为兴而比欤。
臣璧对曰。以流水之潺湲。而喻王室之衰弱。则似是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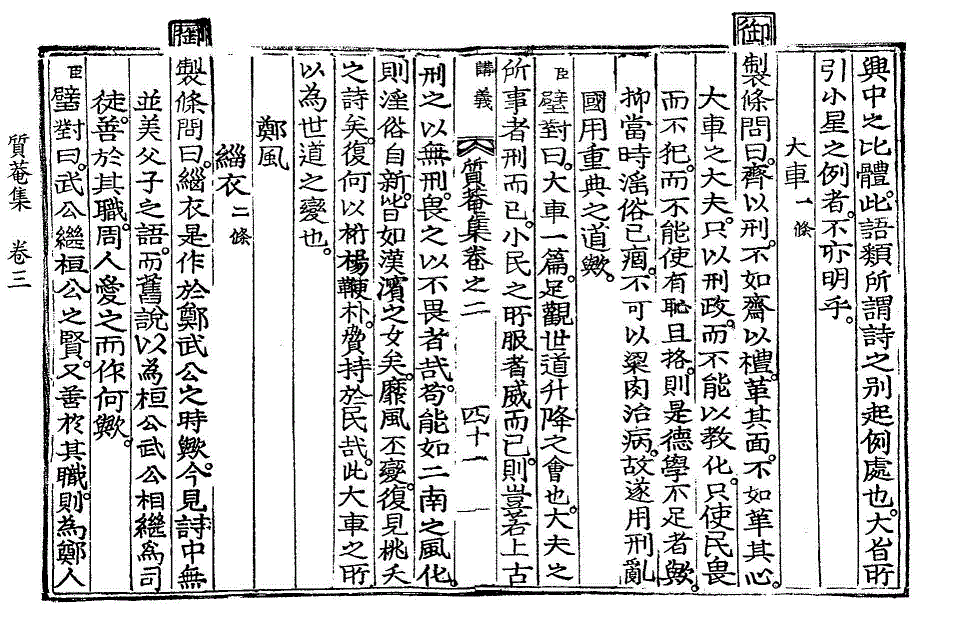 兴中之比体。此语类所谓诗之别起例处也。大旨所引小星之例者。不亦明乎。
兴中之比体。此语类所谓诗之别起例处也。大旨所引小星之例者。不亦明乎。大车(一条)
御制条问曰。齐以刑。不如斋以礼。革其面。不如革其心。大车之大夫。只以刑政。而不能以教化。只使民畏而不犯。而不能使有耻且格。则是德学不足者欤。抑当时淫俗已痼。不可以粱肉治病。故遂用刑乱国用重典之道欤。
臣璧对曰。大车一篇。足观世道升降之会也。大夫之所事者刑而已。小民之所服者威而已。则岂若上古刑之以无刑。畏之以不畏者哉。苟能如二南之风化。则淫俗自新。皆如汉滨之女矣。靡风丕变。复见桃夭之诗矣。复何以桁杨鞭朴。䝱持于民哉。此大车之所以为世道之变也。
郑风
缁衣(二条)
御制条问曰。缁衣是作于郑武公之时欤。今见诗中无并美父子之语。而旧说以为桓公武公相继为司徒。善于其职。周人爱之而作何欤。
臣璧对曰。武公继桓公之贤。又善于其职。则为郑人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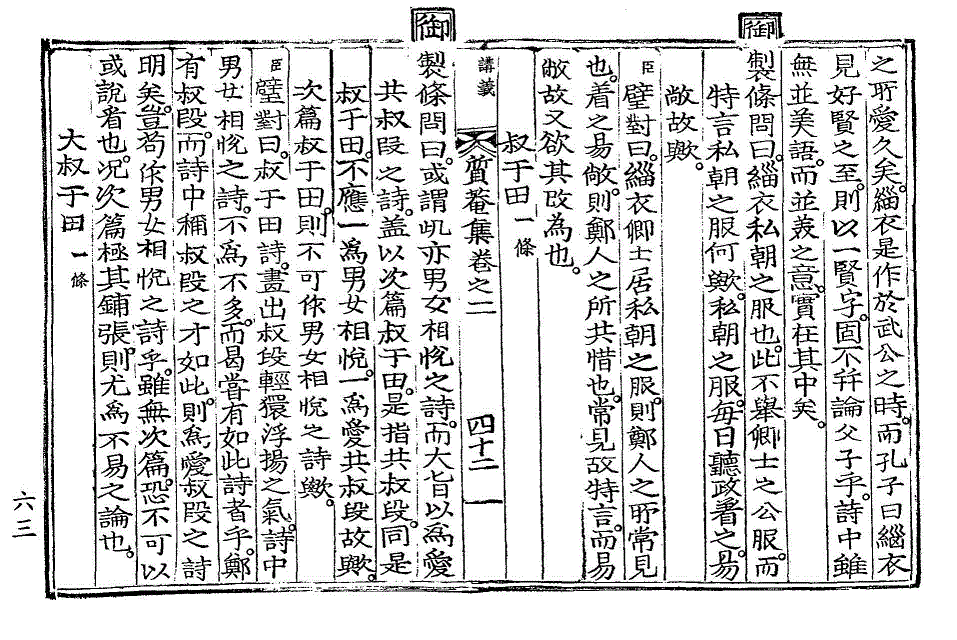 之所爱久矣。缁衣是作于武公之时。而孔子曰缁衣见好贤之至。则以一贤字。固不并论父子乎。诗中虽无并美语。而并美之意。实在其中矣。
之所爱久矣。缁衣是作于武公之时。而孔子曰缁衣见好贤之至。则以一贤字。固不并论父子乎。诗中虽无并美语。而并美之意。实在其中矣。御制条问曰。缁衣私朝之服也。此不举卿士之公服。而特言私朝之服何欤。私朝之服。每日听政着之。易敞故欤。
臣璧对曰。缁衣卿士居私朝之服。则郑人之所常见也。着之易敞。则郑人之所共惜也。常见故特言。而易敝故又欲其改为也。
叔于田(一条)
御制条问曰。或谓此亦男女相悦之诗。而大旨以为爱共叔段之诗。盖以次篇叔于田。是指共叔段。同是叔于田。不应一为男女相悦。一为爱共叔段故欤。次篇叔于田。则不可作男女相悦之诗欤。
臣璧对曰。叔于田诗。画出叔段轻獧浮扬之气。诗中男女相悦之诗。不为不多。而曷尝有如此诗者乎。郑有叔段。而诗中称叔段之才如此。则为爱叔段之诗明矣。岂苟作男女相悦之诗乎。虽无次篇。恐不可以或说看也。况次篇极其铺张。则尤为不易之论也。
大叔于田(一条)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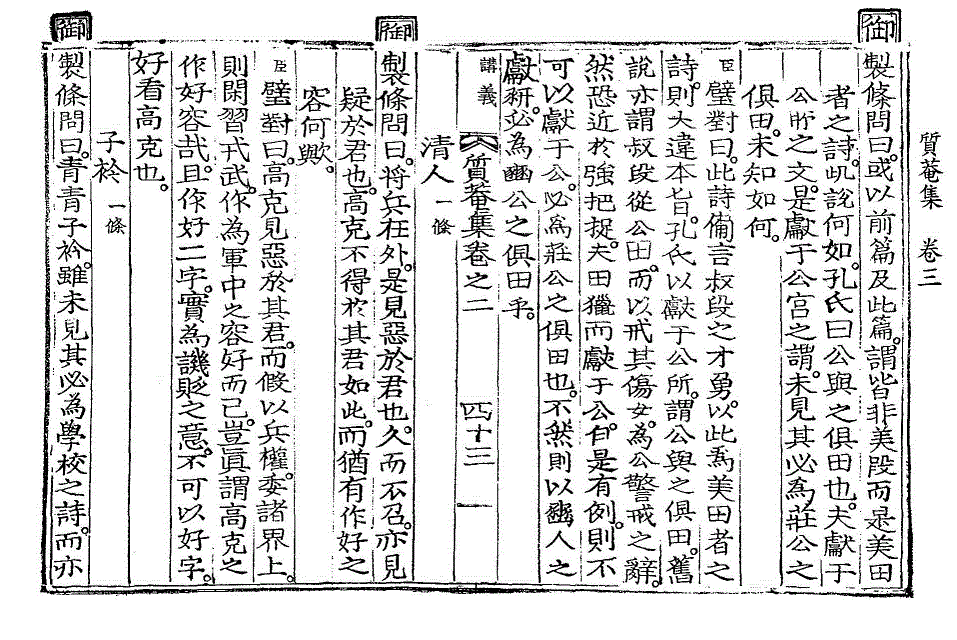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或以前篇及此篇。谓皆非美段而是美田者之诗。此说何如。孔氏曰公与之俱田也。夫献于公所之文。是献于公宫之谓。未见其必为庄公之俱田。未知如何。
御制条问曰。或以前篇及此篇。谓皆非美段而是美田者之诗。此说何如。孔氏曰公与之俱田也。夫献于公所之文。是献于公宫之谓。未见其必为庄公之俱田。未知如何。臣璧对曰。此诗备言叔段之才勇。以此为美田者之诗。则大违本旨。孔氏以献于公所。谓公与之俱田。旧说亦谓叔段从公田。而以戒其伤女。为公警戒之辞。然恐近于强把捉。夫田猎而献于公。自是有例。则不可以献于公。必为庄公之俱田也。不然则以豳人之献豜。必为豳公之俱田乎。
清人(一条)
御制条问曰。将兵在外。是见恶于君也。久而不召。亦见疑于君也。高克不得于其君如此。而犹有作好之容何欤。
臣璧对曰。高克见恶于其君。而假以兵权。委诸界上。则闲习戎武。作为军中之容好而已。岂真谓高克之作好容哉。且作好二字。实为讥贬之意。不可以好字。好看高克也。
子衿(一条)
御制条问曰。青青子衿。虽未见其必为学校之诗。而亦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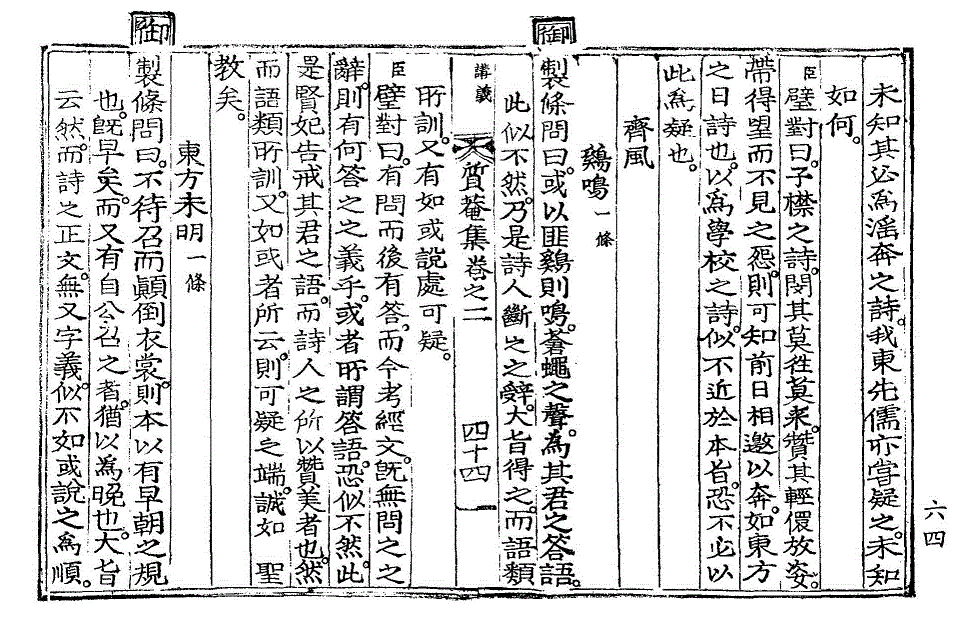 未知其必为淫奔之诗。我东先儒亦尝疑之。未知如何。
未知其必为淫奔之诗。我东先儒亦尝疑之。未知如何。臣璧对曰。子襟之诗。闵其莫往莫来。赞其轻儇放姿。带得望而不见之怨。则可知前日相邀以奔。如东方之日诗也。以为学校之诗。似不近于本旨。恐不必以此为疑也。
齐风
鸡鸣(一条)
御制条问曰。或以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为其君之答语。此似不然。乃是诗人断之之辞。大旨得之。而语类所训。又有如或说处可疑。
臣璧对曰。有问而后有答。而今考经文。既无问之之辞。则有何答之之义乎。或者所谓答语。恐似不然。此是贤妃告戒其君之语。而诗人之所以赞美者也。然而语类所训。又如或者所云。则可疑之端。诚如 圣教矣。
东方未明(一条)
御制条问曰。不待召而颠倒衣裳。则本以有早朝之规也。既早矣。而又有自公召之者。犹以为晚也。大旨云然。而诗之正文。无又字义。似不如或说之为顺。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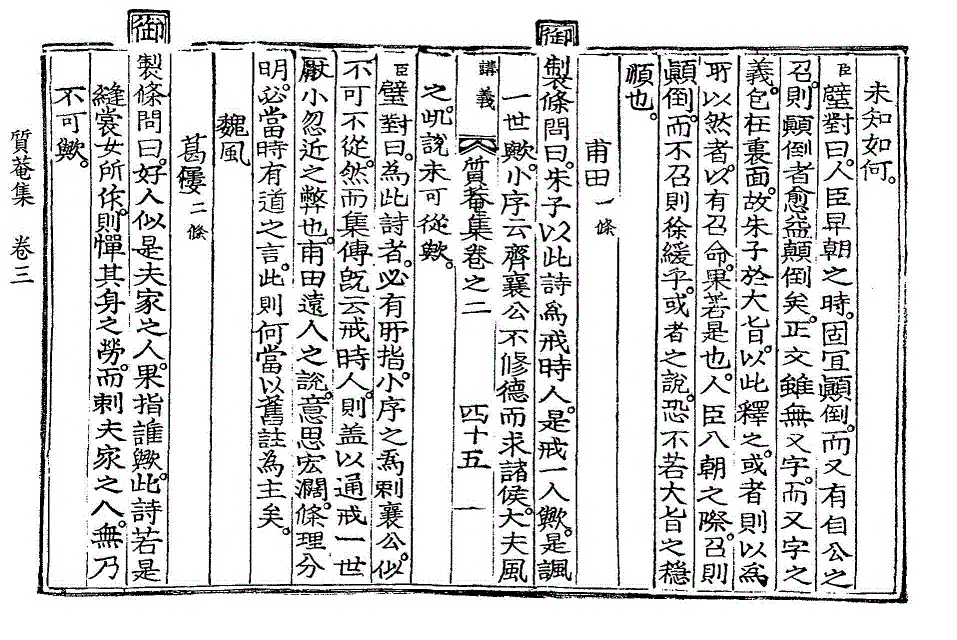 未知如何。
未知如何。臣璧对曰。人臣早朝之时。固宜颠倒。而又有自公之召。则颠倒者愈益颠倒矣。正文虽无又字。而又字之义。包在里面。故朱子于大旨。以此释之。或者则以为所以然者。以有召命。果若是也。人臣入朝之际。召则颠倒。而不召则徐缓乎。或者之说。恐不若大旨之稳顺也。
甫田(一条)
御制条问曰。朱子以此诗为戒时人。是戒一人欤。是讽一世欤。小序云齐襄公不修德而求诸侯。大夫风之。此说未可从欤。
臣璧对曰。为此诗者。必有所指。小序之为刺襄公。似不可不从。然而集传既云戒时人。则盖以通戒一世厌小忽近之弊也。甫田远人之说。意思宏𤄃。条理分明。必当时有道之言。此则何当以旧注为主矣。
魏风
葛屦(二条)
御制条问曰。好人似是夫家之人。果指谁欤。此诗若是缝裳女所作。则惮其身之劳。而刺夫家之人。无乃不可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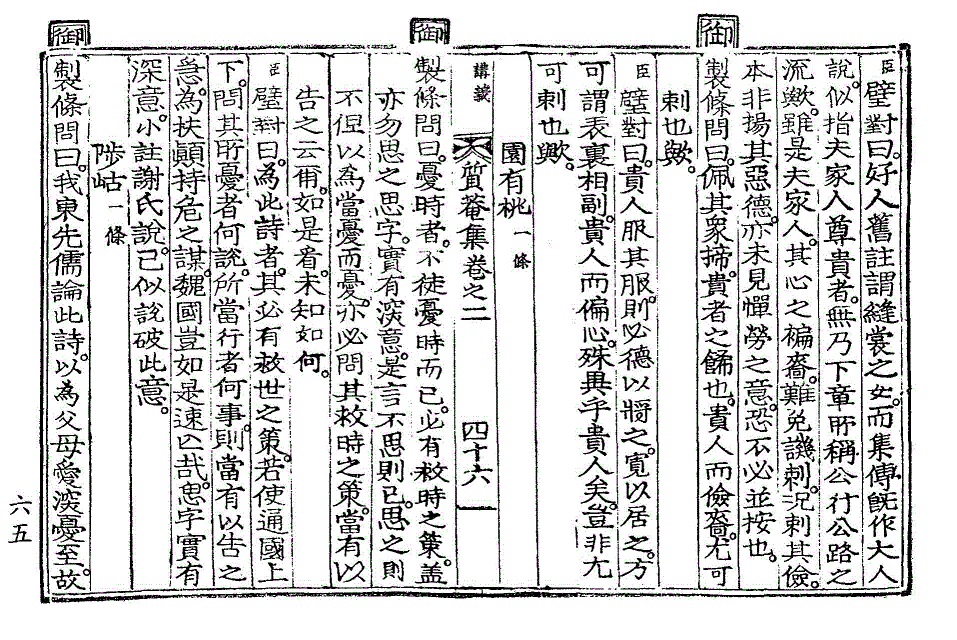 臣璧对曰。好人旧注谓缝裳之女。而集传既作大人说。似指夫家人尊贵者。无乃下章所称公行公路之流欤。虽是夫家人。其心之褊啬。难免讥刺。况刺其俭。本非扬其恶德。亦未见惮劳之意。恐不必并按也。
臣璧对曰。好人旧注谓缝裳之女。而集传既作大人说。似指夫家人尊贵者。无乃下章所称公行公路之流欤。虽是夫家人。其心之褊啬。难免讥刺。况刺其俭。本非扬其恶德。亦未见惮劳之意。恐不必并按也。御制条问曰。佩其众揥。贵者之饰也。贵人而俭啬。尤可刺也欤。
臣璧对曰。贵人服其服。则必德以将之。宽以居之。方可谓表里相副。贵人而偏心。殊异乎贵人矣。岂非尤可刺也欤。
园有桃(一条)
御制条问曰。忧时者。不徒忧时而已。必有救时之策。盖亦勿思之思字。实有深意。是言不思则已。思之则不但以为当忧而忧。亦必问其救时之策。当有以告之云尔。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为此诗者。其必有救世之策。若使通国上下。问其所忧者何说。所当行者何事。则当有以告之急。为扶颠持危之谋。魏国岂如是速亡哉。思字实有深意。小注谢氏。说已似说破此意。
陟岵(一条)
御制条问曰。我东先儒论此诗。以为父母爱深忧至。故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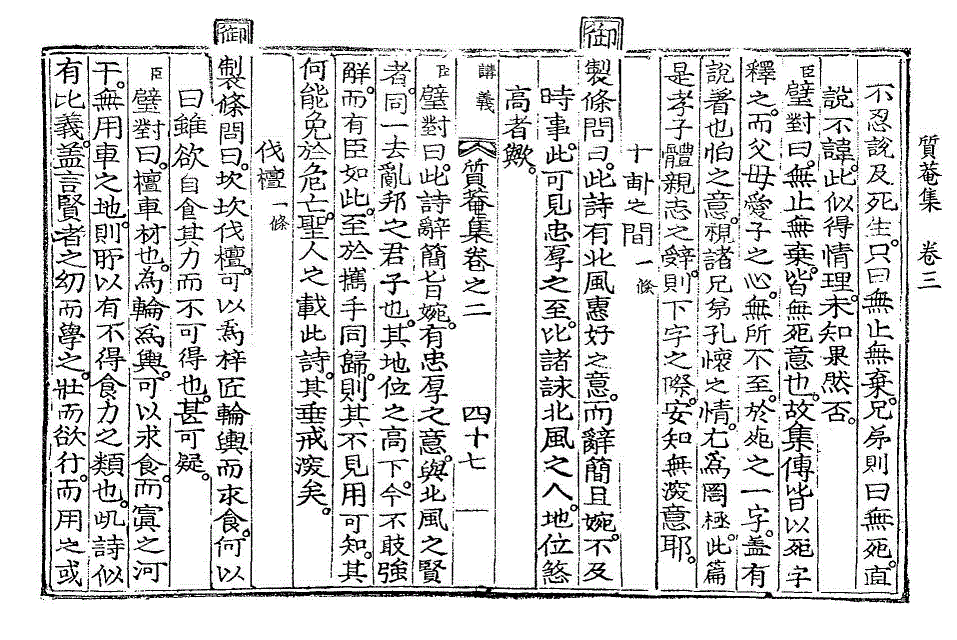 不忍说及死生。只曰无止无弃。兄弟则曰无死。直说不讳。此似得情理。未知果然否。
不忍说及死生。只曰无止无弃。兄弟则曰无死。直说不讳。此似得情理。未知果然否。臣璧对曰。无止无弃。皆无死意也。故集传皆以死字释之。而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于死之一字。盖有说着也怕之意。视诸兄弟孔怀之情。尤为罔极。此篇是孝子体亲志之辞。则下字之际。安知无深意耶。
十亩之间(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有北风惠好之意。而辞简且婉。不及时事。此可见忠厚之至。比诸咏北风之人。地位煞高者欤。
臣璧对曰。此诗辞简旨婉。有忠厚之意。与北风之贤者。同一去乱邦之君子也。其地位之高下。今不敢强解。而有臣如此。至于携手同归。则其不见用可知。其何能免于危亡。圣人之载此诗。其垂戒深矣。
伐檀(一条)
御制条问曰。坎坎伐檀。可以为梓匠轮舆而求食。何以曰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也。甚可疑。
臣璧对曰。檀车材也。为轮为舆。可以求食。而寘之河干。无用车之地。则所以有不得食力之类也。此诗似有比义。盖言贤者之幼而学之。壮而欲行。而用之或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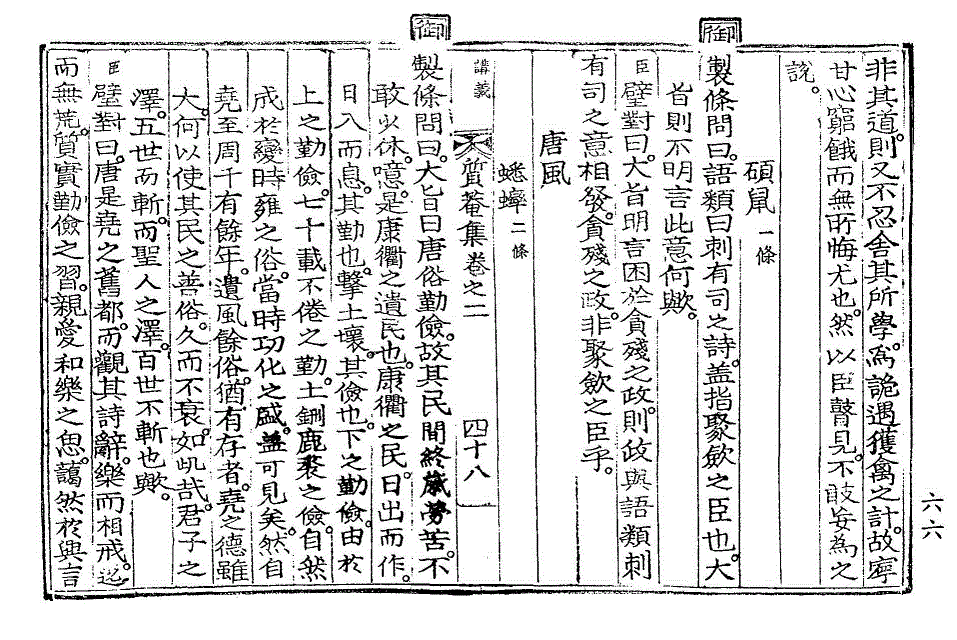 非其道。则又不忍舍其所学。为诡遇获禽之计。故宁甘心穷饿而无所悔尤也。然以臣瞽见。不敢妄为之说。
非其道。则又不忍舍其所学。为诡遇获禽之计。故宁甘心穷饿而无所悔尤也。然以臣瞽见。不敢妄为之说。硕鼠(一条)
御制条问曰。语类曰刺有司之诗。盖指聚敛之臣也。大旨则不明言此意何欤。
臣璧对曰。大旨明言困于贪残之政。则政与语类刺有司之意相发。贪残之政。非聚敛之臣乎。
唐风
蟋蟀(二条)
御制条问曰。大旨曰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噫。是康衢之遗民也。康衢之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勤也。击土坏。其俭也。下之勤俭。由于上之勤俭。七十载不倦之勤。土铏鹿裘之俭。自然成于变时雍之俗。当时功化之盛。盖可见矣。然自尧至周千有馀年。遗风馀俗。犹有存者。尧之德虽大。何以使其民之善俗。久而不衰。如此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圣人之泽。百世不斩也欤。
臣璧对曰。唐是尧之旧都。而观其诗辞。乐而相戒。逸而无荒。质实勤俭之习。亲爱和乐之思。蔼然于兴言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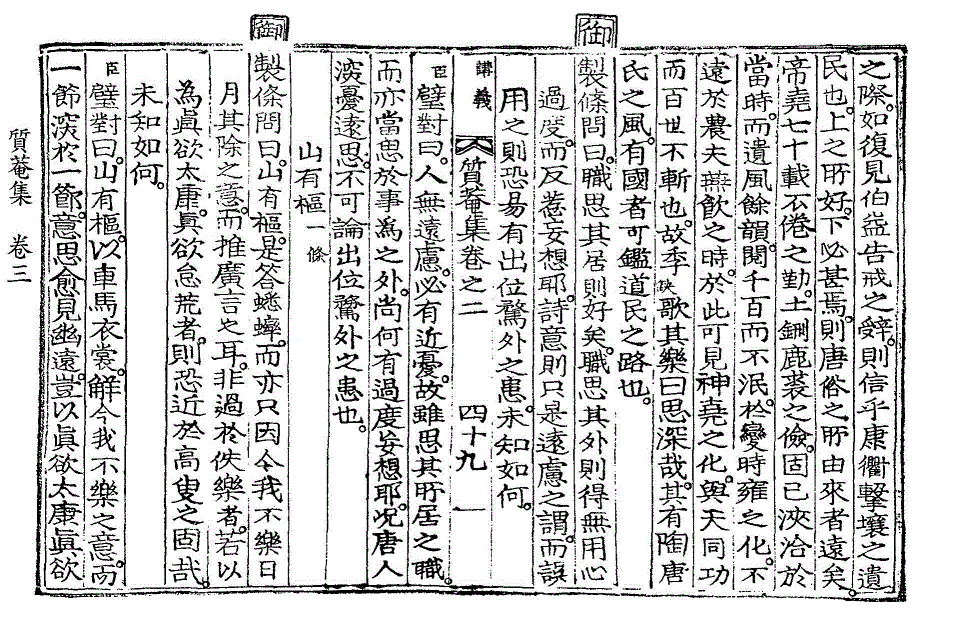 之际。如复见伯益告戒之辞。则信乎康衢击壤之遗民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则唐俗之所由来者远矣。帝尧七十载不倦之勤。土铏鹿裘之俭。固已浃洽于当时。而遗风馀韵。阅千百而不泯。于变时雍之化。不远于农夫燕饮之时。于此可见神尧之化。与天同功而百世不斩也。故季(缺)歌其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风。有国者可鉴道民之路也。
之际。如复见伯益告戒之辞。则信乎康衢击壤之遗民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则唐俗之所由来者远矣。帝尧七十载不倦之勤。土铏鹿裘之俭。固已浃洽于当时。而遗风馀韵。阅千百而不泯。于变时雍之化。不远于农夫燕饮之时。于此可见神尧之化。与天同功而百世不斩也。故季(缺)歌其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风。有国者可鉴道民之路也。御制条问曰。职思其居则好矣。职思其外则得无用心过度。而反惹妄想耶。诗意则只是远虑之谓。而误用之则恐易有出位骛外之患。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虽思其所居之职。而亦当思于事为之外。尚何有过度妄想耶。况唐人深忧远思。不可论出位骛外之患也。
山有枢(一条)
御制条问曰。山有枢。是答蟋蟀。而亦只因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之意。而推广言之耳。非过于佚乐者。若以为真欲太康。真欲怠荒者。则恐近于高叟之固哉。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山有枢。以车马衣裳。解今我不乐之意。而一节深于一节。意思愈见幽远。岂以真欲太康真欲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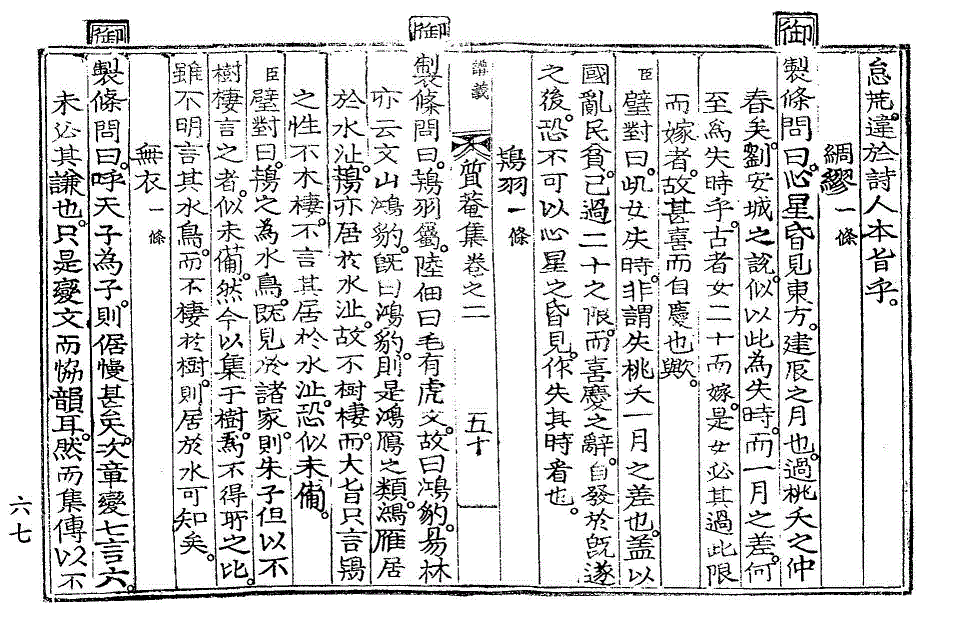 怠荒。违于诗人本旨乎。
怠荒。违于诗人本旨乎。绸缪(一条)
御制条问曰。心星昏见东方。建辰之月也。过桃夭之仲春矣。刘安城之说。似以此为失时。而一月之差。何至为失时乎。古者女二十而嫁。是女必其过此限而嫁者。故甚喜而自庆也欤。
臣璧对曰。此女失时。非谓失桃夭一月之差也。盖以国乱民贫。已过二十之限。而喜庆之辞。自发于既遂之后。恐不可以心星之昏见。作失其时看也。
鸨羽(一条)
御制条问曰。鸨羽属。陆佃曰毛有虎文。故曰鸿豹。易林亦云文山鸿豹。既曰鸿豹。则是鸿雁之类。鸿雁居于水沚。鸨亦居于水沚。故不树栖。而大旨只言鸨之性不木栖。不言其居于水沚。恐似未备。
臣璧对曰。鸨之为水鸟。既见于诸家。则朱子但以不树栖言之者。似未备。然今以集于树。为不得所之比。虽不明言其水鸟。而不栖于树。则居于水可知矣。
无衣(一条)
御制条问曰。呼天子为子。则倨慢甚矣。次章变七言六。未必其谦也。只是变文而协韵耳。然而集传以不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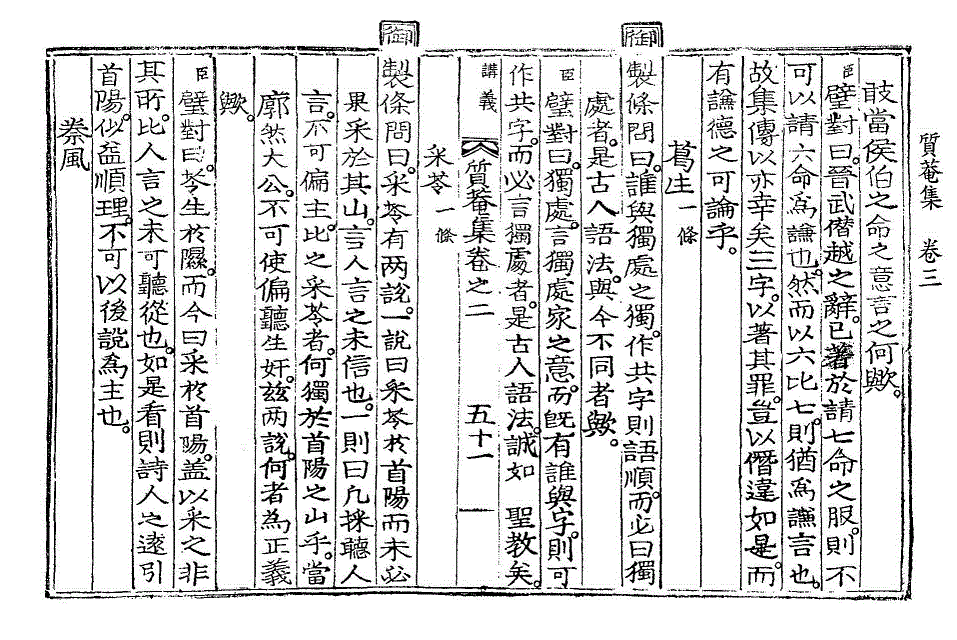 敢当侯伯之命之意言之何欤。
敢当侯伯之命之意言之何欤。臣璧对曰。晋武僭越之辞。已著于请七命之服。则不可以请六命为谦也。然而以六比七。则犹为谦言也。故集传以亦幸矣三字。以著其罪。岂以僭违如是。而有谦德之可论乎。
葛生(一条)
御制条问曰。谁与独处之独。作共字则语顺。而必曰独处者。是古人语法。与今不同者欤。
臣璧对曰。独处。言独处家之意。而既有谁与字。则可作共字。而必言独处者。是古人语法。诚如 圣教矣。
采苓(一条)
御制条问曰。采苓有两说。一说曰采苓于首阳而未必果采于其山。言人言之未信也。一则曰凡采听人言。不可偏主。比之采苓者。何独于首阳之山乎。当廓然大公。不可使偏听生奸。玆两说。何者为正义欤。
臣璧对曰。苓生于隰。而今曰采于首阳。盖以采之非其所。比人言之未可听从也。如是看则诗人之远引首阳。似益顺理。不可以后说为主也。
秦风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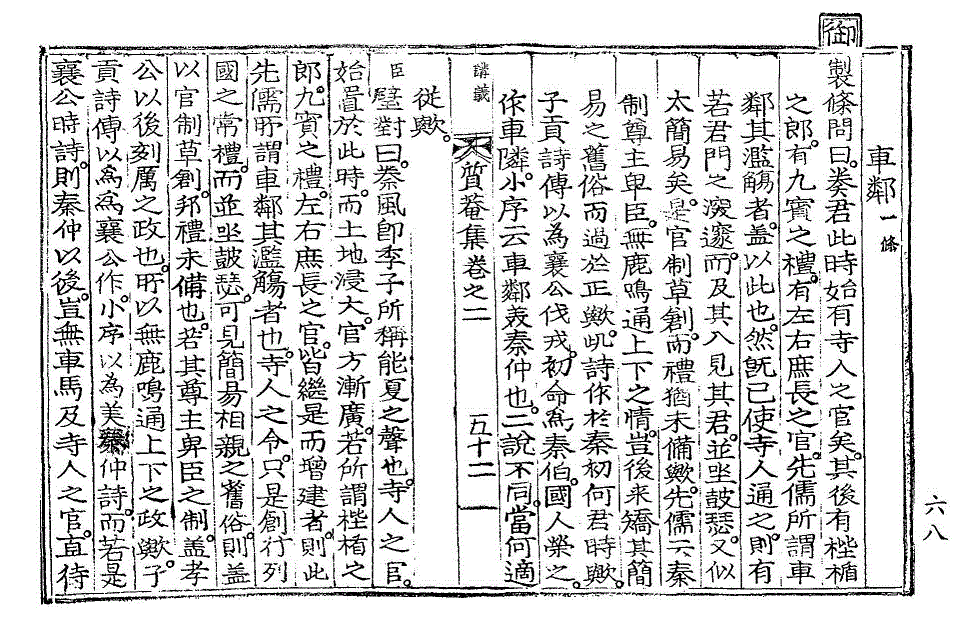 车邻(一条)
车邻(一条)御制条问曰。奏君此时始有寺人之官矣。其后有梐楯之郎。有九宾之礼。有左右庶长之官。先儒所谓车邻其滥觞者。盖以此也。然既已使寺人通之。则有若君门之深邃。而及其入见其君。并坐鼓瑟。又似太简易矣。是官制草创。而礼犹未备欤。先儒云秦制尊主卑臣。无鹿鸣通上下之情。岂后来矫其简易之旧俗而过于正欤。此诗作于秦初何君时欤。子贡诗传以为襄公伐戎。初命为秦伯。国人荣之。作车邻。小序云车邻美秦仲也。二说不同。当何适从欤。
臣璧对曰。秦风即季子所称能夏之声也。寺人之官。始置于此时。而土地浸大。官方渐广。若所谓梐楯之郎。九宾之礼。左右庶长之官。皆继是而增建者。则此先儒所谓车邻其滥觞者也。寺人之令。只是创行列国之常礼。而并坐鼓瑟。可见简易相亲之旧俗。则盖以官制草创。邦礼未备也。若其尊主卑臣之制。盖孝公以后刻厉之政也。所以无鹿鸣通上下之政欤。子贡诗传以为为襄公作。小序以为美秦仲诗。而若是襄公时诗。则秦仲以后。岂无车马及寺人之官。直待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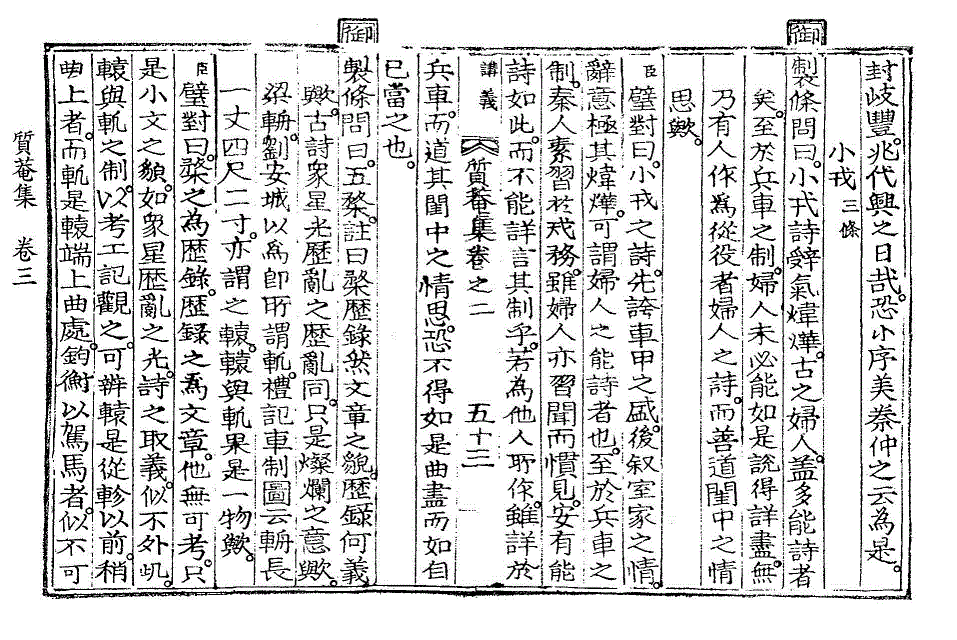 封岐丰。兆代兴之日哉。恐小序美秦仲之云为是。
封岐丰。兆代兴之日哉。恐小序美秦仲之云为是。小戎(三条)
御制条问曰。小戎诗辞气炜烨。古之妇人。盖多能诗者矣。至于兵车之制。妇人未必能如是说得详尽。无乃有人作为从役者妇人之诗。而善道闺中之情思欤。
臣璧对曰。小戎之诗。先誇车甲之盛。后叙室家之情。辞意极其炜烨。可谓妇人之能诗者也。至于兵车之制。秦人素习于戒务。虽妇人亦习闻而惯见。安有能诗如此。而不能详言其制乎。若为他人所作。虽详于兵车。而道其闺中之情思。恐不得如是曲尽而如自己当之也。
御制条问曰。五楘。注曰楘历录然文章之貌。历录何义欤。古诗众星光历乱之历乱同。只是灿烂之意欤。梁辀。刘安城以为即所谓轨。礼记车制图云辀长一丈四尺二寸。亦谓之辕。辕与轨果是一物欤。
臣璧对曰。楘之为历录。历录之为文章。他无可考。只是小文之貌。如众星历乱之光。诗之取义。似不外此。辕与轨之制。以考工记观之。可辨辕是从轸以前。稍曲上者。而轨是辕端上曲处。钧衡以驾马者。似不可
质庵集卷之三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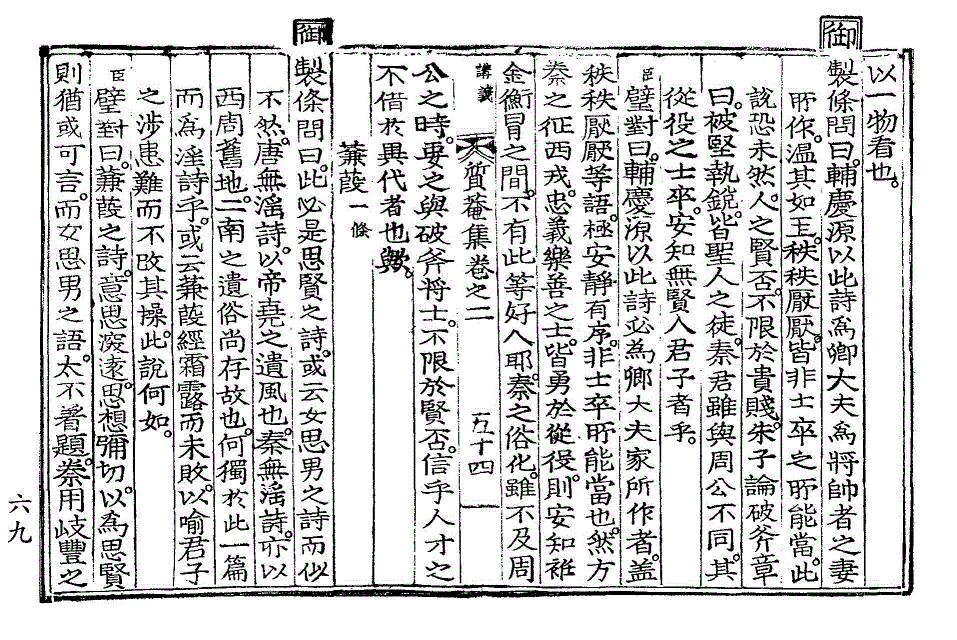 以一物看也。
以一物看也。御制条问曰。辅庆源以此诗为卿大夫为将帅者之妻所作。温其如玉。秩秩厌厌。皆非士卒之所能当。此说恐未然。人之贤否。不限于贵贱。朱子论破斧章曰。被坚执锐。皆圣人之徒。秦君虽与周公不同。其从役之士卒。安知无贤人君子者乎。
臣璧对曰。辅庆源以此诗必为卿大夫家所作者。盖秩秩厌厌等语。极安静有序。非士卒所能当也。然方秦之征西戎。忠义乐善之士。皆勇于从役。则安知衽金衡冒之间。不有此等好人耶。秦之俗化。虽不及周公之时。要之与破斧将士。不限于贤否。信乎人才之不借于异代者也欤。
蒹葭(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必是思贤之诗。或云女思男之诗而似不然。唐无淫诗。以帝尧之遗风也。秦无淫诗。亦以西周旧地。二南之遗俗尚存故也。何独于此一篇而为淫诗乎。或云蒹葭经霜露而未败。以喻君子之涉患难而不改其操。此说何如。
臣璧对曰。蒹葭之诗。意思深远。思想弥切。以为思贤则犹或可言。而女思男之语。太不着题。秦用岐丰之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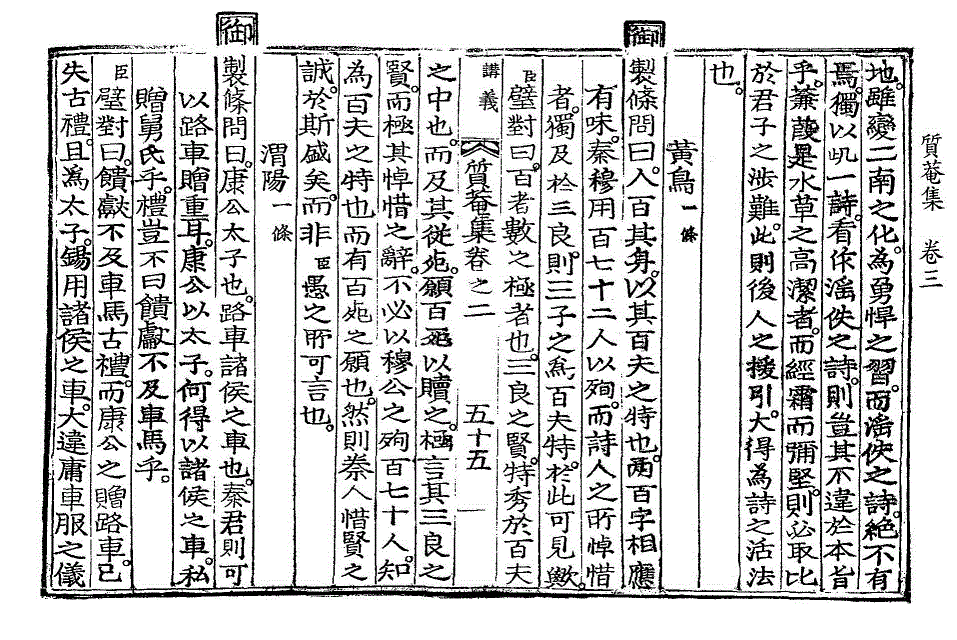 地。虽变二南之化。为勇悍之习。而淫佚之诗。绝不有焉。独以此一诗。看作淫佚之诗。则岂其不违于本旨乎。蒹葭是水草之高洁者。而经霜而弥坚。则必取比于君子之涉难。此则后人之援引。大得为诗之活法也。
地。虽变二南之化。为勇悍之习。而淫佚之诗。绝不有焉。独以此一诗。看作淫佚之诗。则岂其不违于本旨乎。蒹葭是水草之高洁者。而经霜而弥坚。则必取比于君子之涉难。此则后人之援引。大得为诗之活法也。黄鸟(一条)
御制条问曰。人百其身。以其百夫之特也。两百字相应有味。秦穆用百七十二人以殉。而诗人之所悼惜者。独及于三良。则三子之为百夫特。于此可见欤。
臣璧对曰。百者数之极者也。三良之贤。特秀于百夫之中也。而及其从死。愿百死以赎之。极言其三良之贤。而极其悼惜之辞。不必以穆公之殉百七十人。知为百夫之特也而有百死之愿也。然则秦人惜贤之诚。于斯盛矣。而非臣愚之所可言也。
渭阳(一条)
御制条问曰。康公太子也。路车诸侯之车也。秦君则可以路车赠重耳。康公以太子。何得以诸侯之车。私赠舅氏乎。礼岂不曰馈献不及车马乎。
臣璧对曰。馈献不及车马古礼。而康公之赠路车。已失古礼。且为太子。锡用诸侯之车。大违庸车服之仪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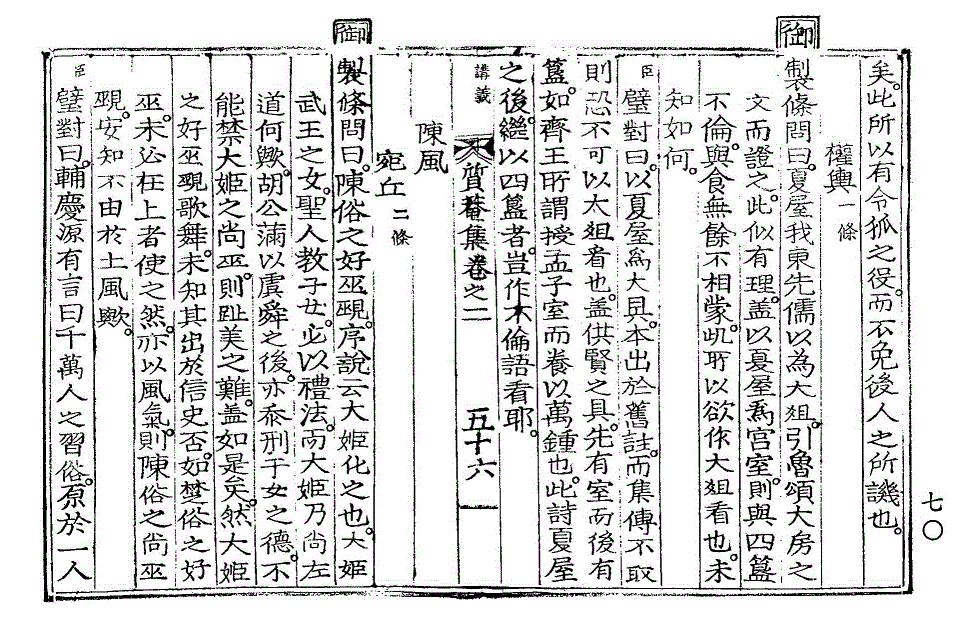 矣。此所以有令狐之役。而不免后人之所讥也。
矣。此所以有令狐之役。而不免后人之所讥也。权舆(一条)
御制条问曰。夏屋我东先儒以为大俎。引鲁颂大房之文而證之。此似有理。盖以夏屋为宫室。则与四簋不伦。与食无馀不相蒙。此所以欲作大俎看也。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以夏屋为大具。本出于旧注。而集传不取则恐不可以大俎看也。盖供贤之具。先有室而后有簋。如齐王所谓授孟子室而养以万钟也。此诗夏屋之后。继以四簋者。岂作不伦语看耶。
陈风
宛丘(二条)
御制条问曰。陈俗之好巫觋。序说云大姬化之也。大姬武王之女。圣人教子女。必以礼法。而大姬乃尚左道何欤。胡公满以虞舜之后。亦忝刑于女之德。不能禁大姬之尚巫。则趾美之难。盖如是矣。然大姬之好巫觋歌舞。未知其出于信史否。如楚俗之好巫。未必在上者使之然。亦以风气。则陈俗之尚巫觋。安知不由于土风欤。
臣璧对曰。辅庆源有言曰千万人之习俗。原于一人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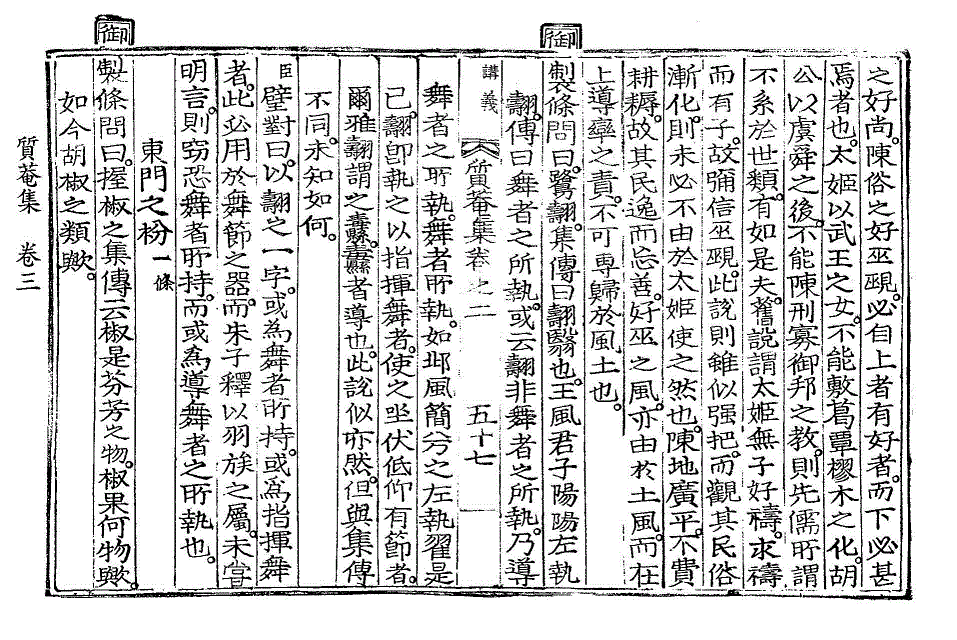 之好尚。陈俗之好巫觋。必自上者有好者。而下必甚焉者也。太姬以武王之女。不能敷葛覃樛木之化。胡公以虞舜之后不能陈刑寡御邦之教。则先儒所谓不系于世类。有如是夫。旧说谓太姬无子好祷。求祷而有子。故弥信巫觋。此说则虽似强把。而观其民俗渐化。则未必不由于太姬使之然也。陈地广平。不费耕耨。故其民逸而忘善。好巫之风。亦由于土风。而在上导率之责。不可专归于风土也。
之好尚。陈俗之好巫觋。必自上者有好者。而下必甚焉者也。太姬以武王之女。不能敷葛覃樛木之化。胡公以虞舜之后不能陈刑寡御邦之教。则先儒所谓不系于世类。有如是夫。旧说谓太姬无子好祷。求祷而有子。故弥信巫觋。此说则虽似强把。而观其民俗渐化。则未必不由于太姬使之然也。陈地广平。不费耕耨。故其民逸而忘善。好巫之风。亦由于土风。而在上导率之责。不可专归于风土也。御制条问曰。鹭翿。集传曰翿翳也。王风君子阳阳左执翿。传曰舞者之所执。或云翿非舞者之所执。乃导舞者之所执。舞者所执。如邶风简兮之左执翟是已。翿即执之以指挥舞者。使之坐伏低仰有节者。尔雅翿谓之纛。纛者导也。此说似亦然。但与集传不同。未知如何。
臣璧对曰。以翿之一字。或为舞者所持。或为指挥舞者。此必用于舞节之器。而朱子释以羽族之属。未尝明言。则窃恐舞者所持。而或为导舞者之所执也。
东门之枌(一条)
御制条问曰。握椒之集传云椒是芬芳之物。椒果何物欤。如今胡椒之类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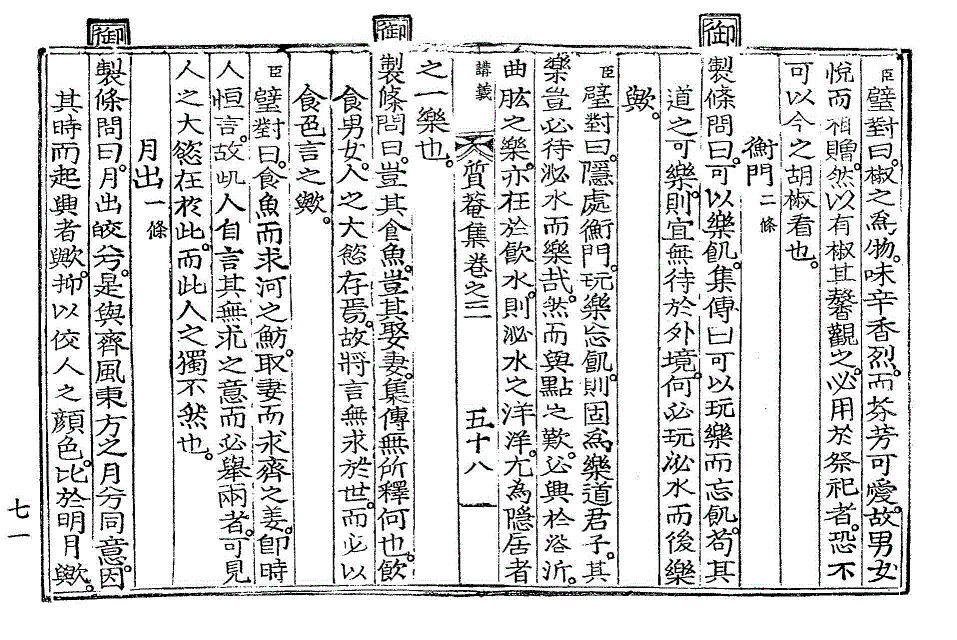 臣璧对曰。椒之为物。味辛香烈。而芬芳可爱。故男女悦而相赠。然以有椒其馨观之。必用于祭祀者。恐不可以今之胡椒看也。
臣璧对曰。椒之为物。味辛香烈。而芬芳可爱。故男女悦而相赠。然以有椒其馨观之。必用于祭祀者。恐不可以今之胡椒看也。衡门(二条)
御制条问曰。可以乐饥。集传曰可以玩乐而忘饥。苟其道之可乐。则宜无待于外境。何必玩泌水而后乐欤。
臣璧对曰。隐处衡门。玩乐忘饥。则固为乐道君子。其乐岂必待泌水而乐哉。然而与点之叹。必兴于浴沂。曲肱之乐。亦在于饮水。则泌水之洋洋。尤为隐居者之一乐也。
御制条问曰。岂其食鱼。岂其娶妻。集传无所释何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将言无求于世。而必以食色言之欤。
臣璧对曰。食鱼而求河之鲂。取妻而求齐之姜。即时人恒言。故此人自言其无求之意而必举两者。可见人之大欲在于此。而此人之独不然也。
月出(一条)
御制条问曰。月出皎兮。是与齐风东方之月兮同意。因其时而起兴者欤。抑以佼人之颜色。比于明月欤。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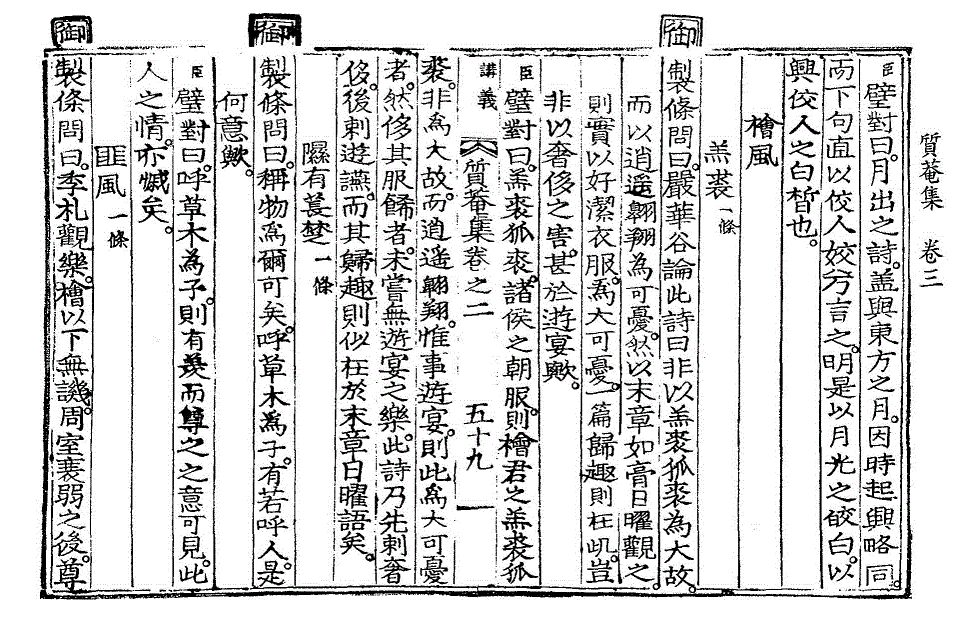 臣璧对曰。月出之诗。盖与东方之月。因时起兴略同。而下句直以佼人姣兮言之。明是以月光之皎白。以兴佼人之白晰也。
臣璧对曰。月出之诗。盖与东方之月。因时起兴略同。而下句直以佼人姣兮言之。明是以月光之皎白。以兴佼人之白晰也。桧风
羔裘(一条)
御制条问曰。严华谷论此诗曰非以羔裘狐裘为大故。而以逍遥翱翔为可忧。然以末章如膏日曜观之。则实以好洁衣服。为大可忧。一篇归趣则在此。岂非以奢侈之害。甚于游宴欤。
臣璧对曰。羔裘狐裘。诸侯之朝服。则桧君之羔裘狐裘。非为大故。而逍遥翱翔。惟事游宴。则此为大可忧者。然侈其服饰者。未尝无游宴之乐。此诗乃先刺奢侈。后刺游宴。而其归趣则似在于末章日曜语矣。
隰有苌楚(一条)
御制条问曰。称物为尔可矣。呼草木为子。有若呼人。是何意欤。
臣璧对曰。呼草木为子。则有羡而尊之之意可见。此人之情。亦戚矣。
匪风(一条)
御制条问曰。季札观乐。桧以下无讥。周室衰弱之后。尊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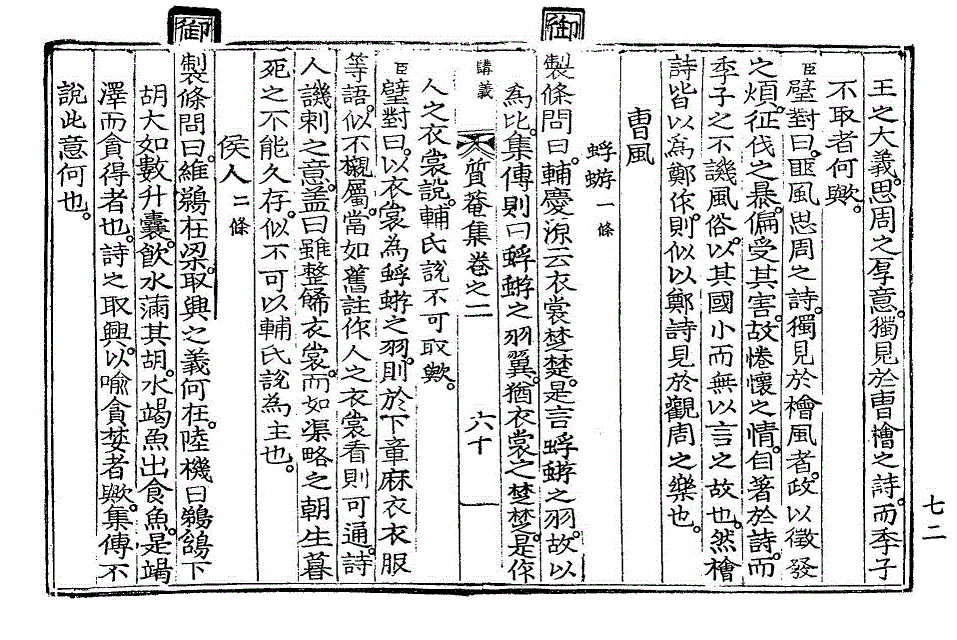 王之大义。思周之厚意。独见于曹桧之诗。而季子不取者何欤。
王之大义。思周之厚意。独见于曹桧之诗。而季子不取者何欤。臣璧对曰。匪风思周之诗。独见于桧风者。政以徵发之烦。征伐之暴。偏受其害。故惓怀之情。自著于诗。而季子之不讥风俗。以其国小而无以言之故也。然桧诗皆以为郑作。则似以郑诗见于观周之乐也。
曹风
蜉蝣(一条)
御制条问曰。辅庆源云衣裳楚楚。是言蜉蝣之羽。故以为比。集传则曰蜉蝣之羽翼。犹衣裳之楚楚。是作人之衣裳说。辅氏说不可取欤。
臣璧对曰。以衣裳为蜉蝣之羽。则于下章麻衣衣服等语。似不榇属。当如旧注作人之衣裳看则可通。诗人讥刺之意。盖曰虽整饰衣裳。而如渠略之朝生暮死之不能久存。似不可以辅氏说为主也。
候人(二条)
御制条问曰。维鹈在梁。取兴之义何在。陆机曰鹈𪁟下胡大如数升囊。饮水满其胡。水竭鱼出食鱼。是竭泽而贪得者也。诗之取兴。以喻贪婪者欤。集传不说此意何也。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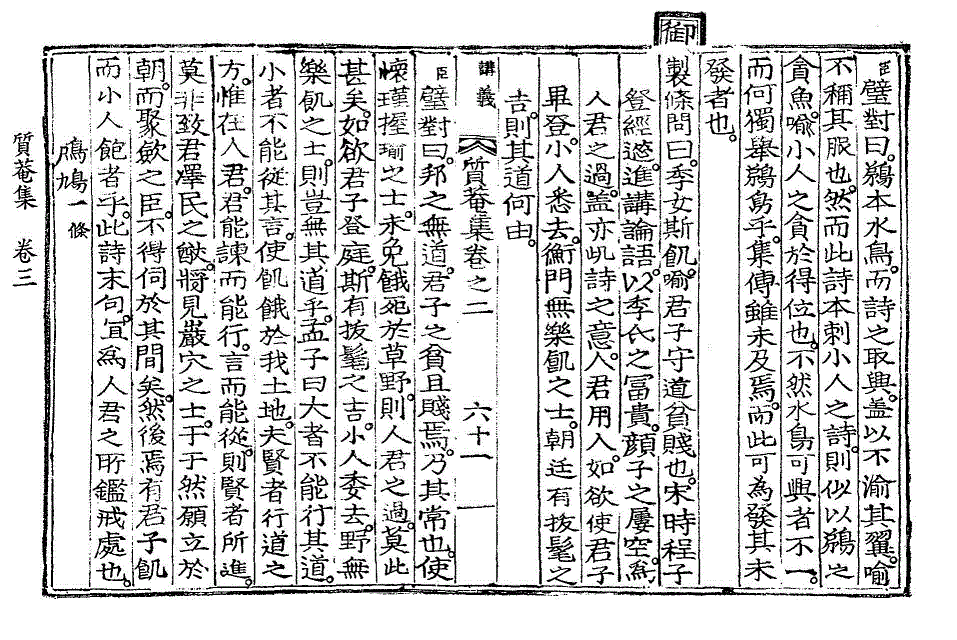 臣璧对曰。鹈本水鸟。而诗之取兴。盖以不渝其翼。喻不称其服也。然而此诗本刺小人之诗。则似以鹈之贪鱼。喻小人之贪于得位也。不然水鸟可兴者不一。而何独举鹈鸟乎。集传虽未及焉。而此可为发其未发者也。
臣璧对曰。鹈本水鸟。而诗之取兴。盖以不渝其翼。喻不称其服也。然而此诗本刺小人之诗。则似以鹈之贪鱼。喻小人之贪于得位也。不然水鸟可兴者不一。而何独举鹈鸟乎。集传虽未及焉。而此可为发其未发者也。御制条问曰。季女斯饥。喻君子守道贫贱也。宋时程子登经筵。进讲论语。以季氏之富贵。颜子之屡空。为人君之过。盖亦此诗之意。人君用人。如欲使君子毕登。小人悉去。衡门无乐饥之士。朝廷有拔髦之吉。则其道何由。
臣璧对曰。邦之无道。君子之贫且贱焉。乃其常也。使怀瑾握瑜之士。未免饿死于草野。则人君之过。莫此甚矣。如欲君子登庭。斯有拔髦之吉。小人委去。野无乐饥之士。则岂无其道乎。孟子曰大者不能行其道。小者不能从其言。使饥饿于我土地。夫贤者行道之方。惟在人君。君能谏而能行。言而能从。则贤者所进。莫非致君凙民之猷。将见岩穴之士。于于然愿立于朝。而聚敛之臣。不得伺于其间矣。然后焉有君子饥而小人饱者乎。此诗末句。宜为人君之所鉴戒处也。
鸤鸠(一条)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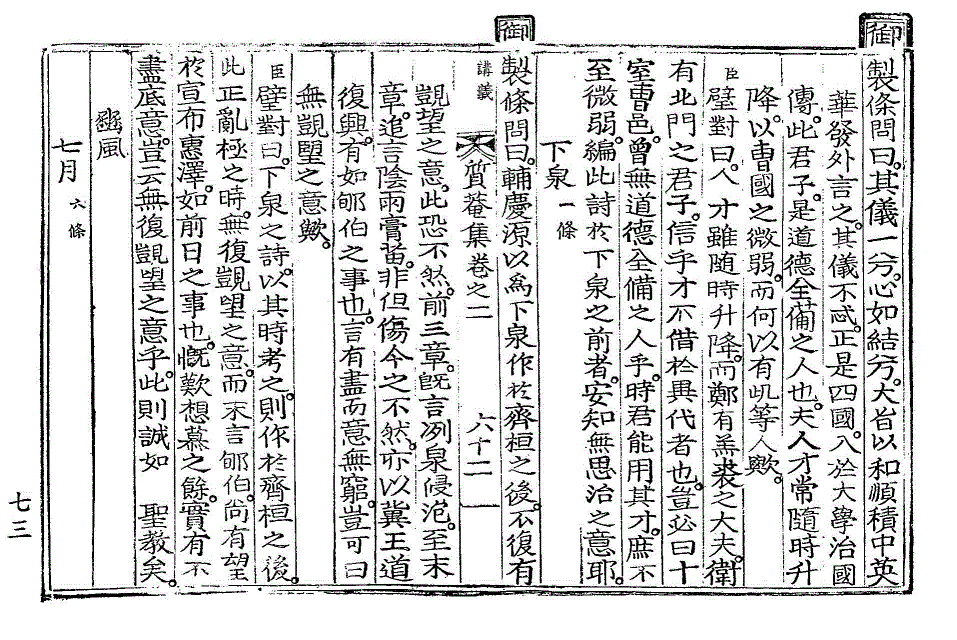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大旨以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言之。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入于大学治国传。此君子。是道德全备之人也。夫人才常随时升降。以曹国之微弱。而何以有此等人欤。
御制条问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大旨以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言之。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入于大学治国传。此君子。是道德全备之人也。夫人才常随时升降。以曹国之微弱。而何以有此等人欤。臣璧对曰。人才虽随时升降。而郑有羔裘之大夫。卫有北门之君子。信乎才不借于异代者也。岂必曰十室曹邑。曾无道德全备之人乎。时君能用其才。庶不至微弱。编此诗于下泉之前者。安知无思治之意耶。
下泉(一条)
御制条问曰。辅庆源以为下泉作于齐桓之后。不复有觊望之意。此恐不然。前三章。既言冽泉侵泡。至末章。追言阴雨膏苗。非但伤今之不然。亦以冀王道复兴。有如郇伯之事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岂可曰无觊望之意欤。
臣璧对曰。下泉之诗。以其时考之。则作于齐桓之后。此正乱极之时。无复觊望之意。而末言郇伯。尚有望于宣布惠泽。如前日之事也。慨叹想慕之馀。实有不尽底意。岂云无复觊望之意乎。此则诚如 圣教矣。
豳风
七月(六条)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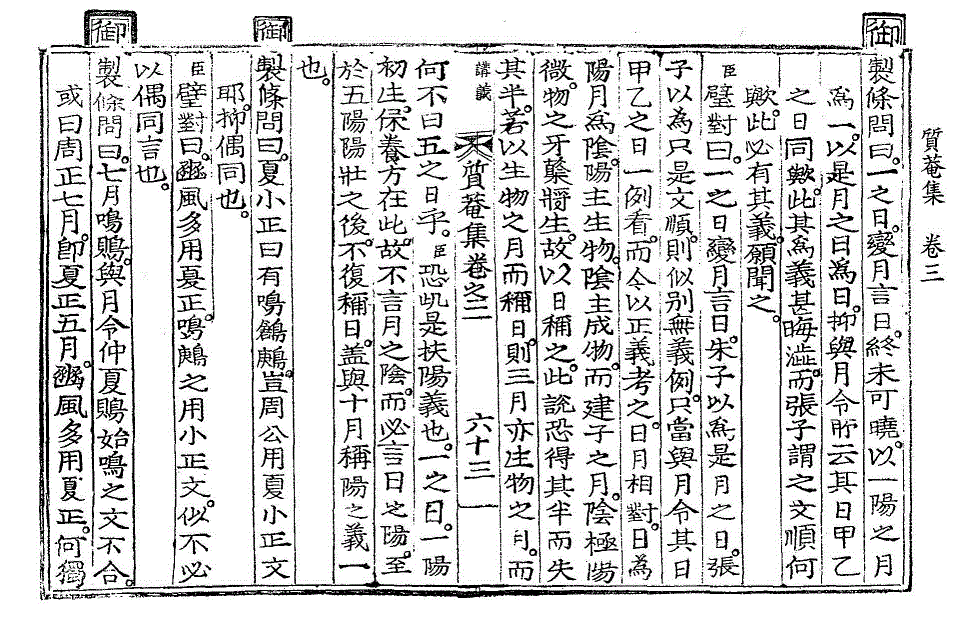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一之日。变月言日。终未可晓。以一阳之月为一。以是月之日为日。抑与月令所云其日甲乙之日同欤。此其为义甚晦涩。而张子谓之文顺何欤。此必有其义。愿闻之。
御制条问曰。一之日。变月言日。终未可晓。以一阳之月为一。以是月之日为日。抑与月令所云其日甲乙之日同欤。此其为义甚晦涩。而张子谓之文顺何欤。此必有其义。愿闻之。臣璧对曰。一之日变月言日。朱子以为是月之日。张子以为只是文顺。则似别无义例。只当与月令其日甲乙之日一例看。而今以正义考之。日月相对。日为阳月为阴。阳主生物。阴主成物。而建子之月。阴极阳微。物之牙蘖将生。故以日称之。此说恐得其半而失其半。若以生物之月而称日。则三月亦生物之月。而何不曰五之日乎。臣恐此是扶阳义也。一之日。一阳初生。保养方在此。故不言月之阴。而必言日之阳。至于五阳阳壮之后。不复称日。盖与十月称阳之义一也。
御制条问曰。夏小正曰有鸣鸧鹒。岂周公用夏小正文耶。抑偶同也。
臣璧对曰。豳风多用夏正。鸣鹒之用小正文。似不必以偶同言也。
御制条问曰。七月鸣鵙。与月令仲夏鵙始鸣之文不合。或曰周正七月。即夏正五月。豳风多用夏正。何独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4L 页
 于此。一物而用周正欤。王肃断以七月为五月之误。未知是否。
于此。一物而用周正欤。王肃断以七月为五月之误。未知是否。臣璧对曰。鵙鸣于仲夏。而此云七月。或谓豳地晚寒。至七月始鸣。此亦可通。然鵙之鸣。始于五月。而或至于七月。言于七月者。正以起八月载绩之候也。王氏之断以五月。似近于强把着也。
御制条问曰。为公子裳。承采蘩而言。然而猎者之取狐狸。不言为豳公之裘。必言为公子裘何欤。
臣璧对曰。诗是豳人之诗。而公子乃豳之公子。则不言豳公。必言公子。犹言吾君之子。尤以见亲近之意也。
御制条问曰。曰为改岁。终是可疑。豳公时。未必迭用三正。如吕东莱说。私记其时月。虽有朱子说。恐亦非定论。未知如何说。方为可通欤。
臣璧对曰。豳公创国偏方。未有正朔之用例。则三正之通于民俗久矣。以十月为改岁。已有诸家训释。而当以刘安城说看得矣。
御制条问曰。跻堂称觥。可见当时之礼野意真。而但未知适然欤。抑每岁如此欤。是必风俗真率。其始以忠爱之心。民自为之。而豳君受之。后世遂以为常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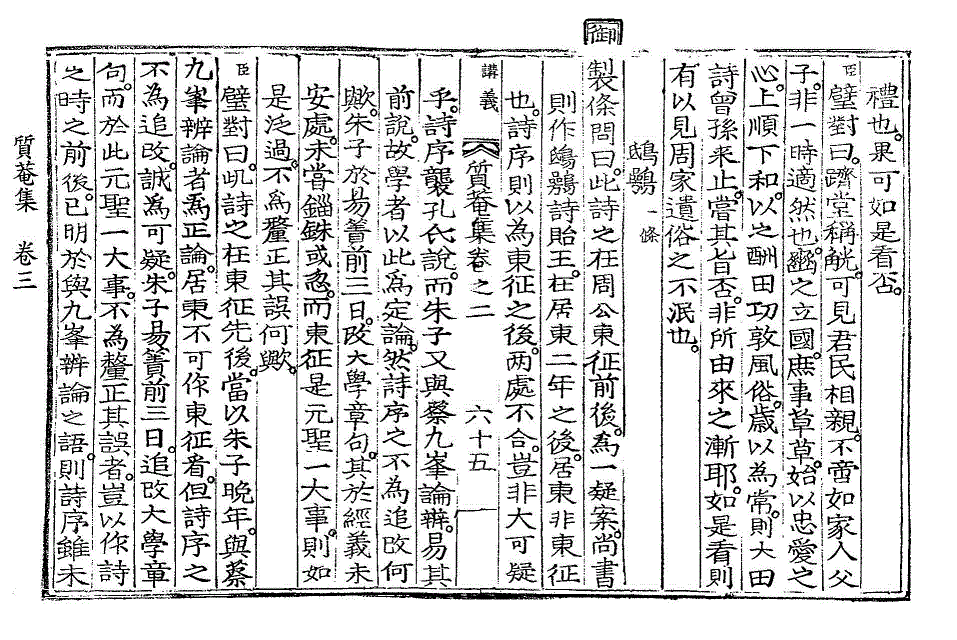 礼也。果可如是看否。
礼也。果可如是看否。臣璧对曰。跻堂称觥。可见君民相亲。不啻如家人父子。非一时适然也。豳之立国。庶事草草。始以忠爱之心。上顺下和。以之酬田功敦风俗。岁以为常。则大田诗曾孙来止。尝其旨否。非所由来之渐耶。如是看则有以见周家遗俗之不泯也。
鸱鹗(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之在周公东征前后。为一疑案。尚书则作鸱鹗诗贻王。在居东二年之后。居东非东征也。诗序则以为东征之后。两处不合。岂非大可疑乎。诗序袭孔氏说。而朱子又与蔡九峰论辨。易其前说。故学者以此为定论。然诗序之不为追改何欤。朱子于易箦前三日。改大学章句。其于经义未安处。未尝锱铢或忽。而东征是元圣一大事。则如是泛过。不为釐正其误何欤。
臣璧对曰。此诗之在东征先后。当以朱子晚年。与蔡九峰辨论者为正论。居东不可作东征看。但诗序之不为追改。诚为可疑。朱子易箦前三日。追改大学章句。而于此元圣一大事。不为釐正其误者。岂以作诗之时之前后。已明于与九峰辨论之语。则诗序虽未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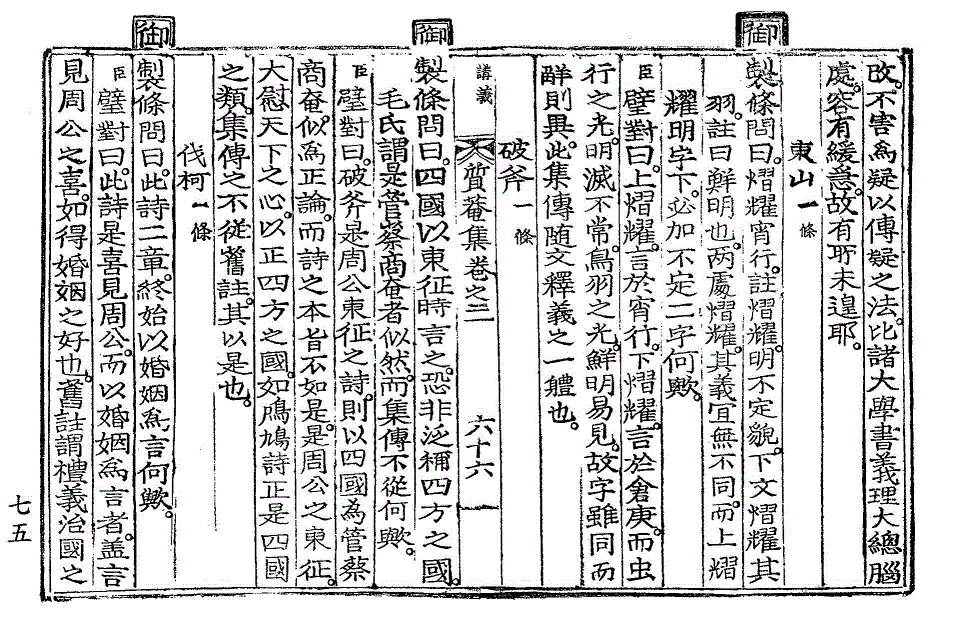 改。不害为疑以传疑之法。比诸大学书义理大总脑处。容有缓急。故有所未遑耶。
改。不害为疑以传疑之法。比诸大学书义理大总脑处。容有缓急。故有所未遑耶。东山(一条)
御制条问曰。熠耀宵行。注熠耀。明不定貌。下文熠耀其羽。注曰鲜明也。两处熠耀。其义宜无不同。而上熠耀明字下。必加不定二字何欤。
臣璧对曰。上熠耀。言于宵行。下熠耀。言于仓庚。而虫行之光。明灭不常。鸟羽之光。鲜明易见。故字虽同而解则异。此集传随文释义之一体也。
破斧(一条)
御制条问曰。四国以东征时言之。恐非泛称四方之国。毛氏谓是管蔡商奄者似然。而集传不从何欤。
臣璧对曰。破斧是周公东征之诗。则以四国为管蔡商奄。似为正论。而诗之本旨不如是。是周公之东征。大慰天下之心。以正四方之国。如鸤鸠诗正是四国之类。集传之不从旧注。其以是也。
伐柯(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二章。终始以婚姻为言何欤。
臣璧对曰。此诗是喜见周公。而以婚姻为言者。盖言见周公之喜。如得婚姻之好也。旧注谓礼义治国之
质庵集卷之三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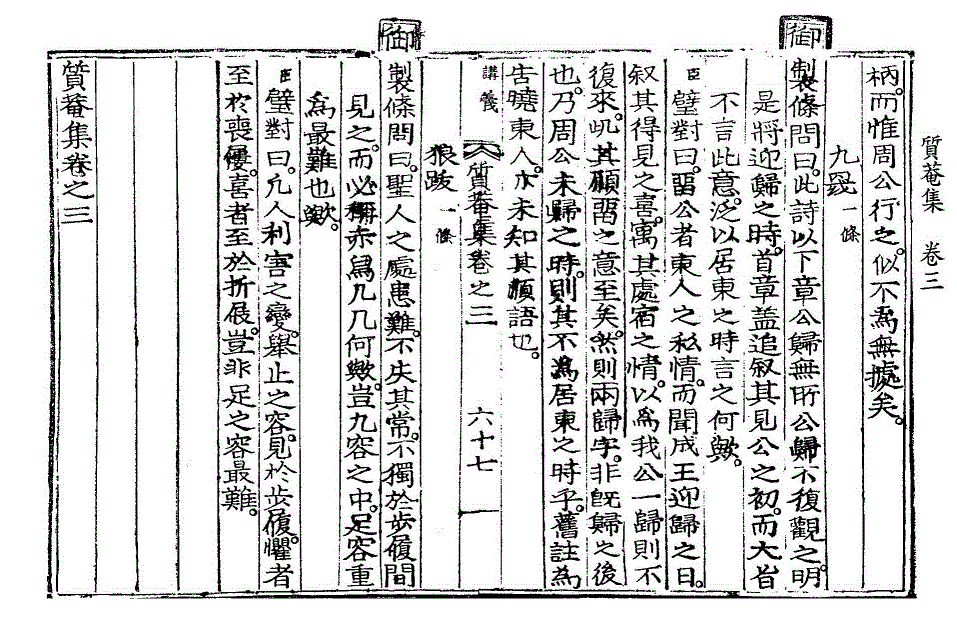 柄。而惟周公行之。似不为无据矣。
柄。而惟周公行之。似不为无据矣。九罭(一条)
御制条问曰。此诗以下章公归无所公归不复观之。明是将迎归之时。首章盖追叙其见公之初。而大旨不言此意。泛以居东之时言之何欤。
臣璧对曰。留公者东人之私情。而闻成王迎归之日。叙其得见之喜。寓其处宿之情。以为我公一归则不复来。此其愿留之意至矣。然则两归字。非既归之后也。乃周公未归之时。则其不为居东之时乎。旧注为告晓东人。亦未知其顺语也。
狼跋(一条)
御制条问曰。圣人之处患难。不失其常。不独于步履间见之。而必称赤舄几几何欤。岂九容之中。足容重为最难也欤。
臣璧对曰。凡人利害之变。举止之容。见于步履。惧者至于丧履。喜者至于折屐。岂非足之容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