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录
附录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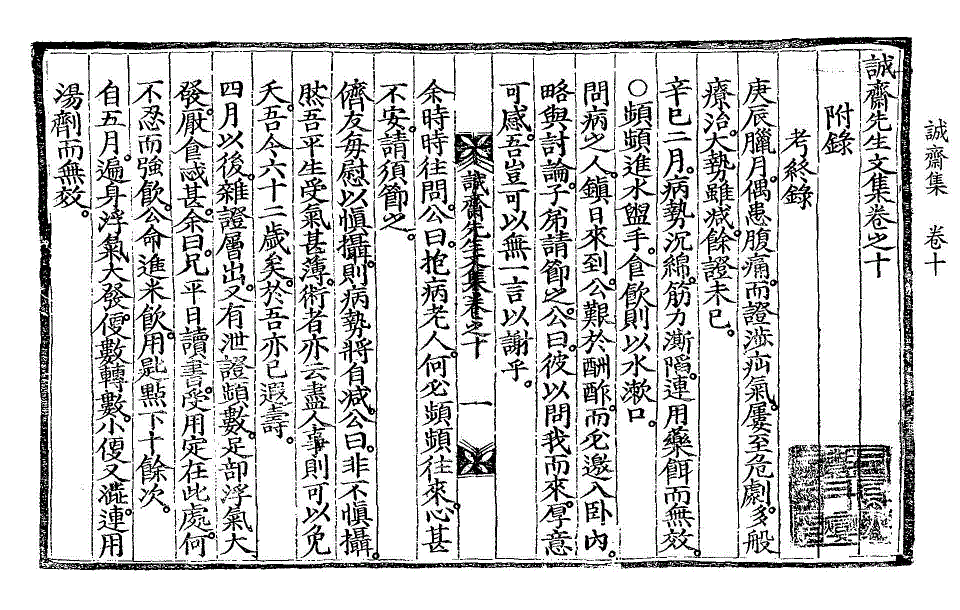 考终录[柳栻]
考终录[柳栻]庚辰腊月。偶患腹痛。而證涉疝气。屡至危剧。多般疗治。大势虽减。馀證未已。
辛巳二月。病势沉绵。筋力澌陷。连用药饵而无效。
○频频进水盥手。食饮则以水漱口。
问病之人。镇日来到。公艰于酬酢。而必邀入卧内。略与讨论。子弟请节之。公曰。彼以问我而来。厚意可感。吾岂可以无一言以谢乎。
余时时往问。公曰。抱病老人。何必频频往来。心甚不安。请须节之。
侪友每慰以慎摄。则病势将自减。公曰。非不慎摄。然吾平生受气甚薄。术者亦云尽人事则可以免夭。吾今六十二岁矣。于吾亦已遐寿。
四月以后。杂證层出。又有泄證频数。足部浮气大发。厌食忒甚。余曰。兄平日读书。受用定在此处。何不忍而强饮。公命进米饮。用匙点下十馀次。
自五月。遍身浮气大发。便数转数。小便又涩。连用汤剂而无效。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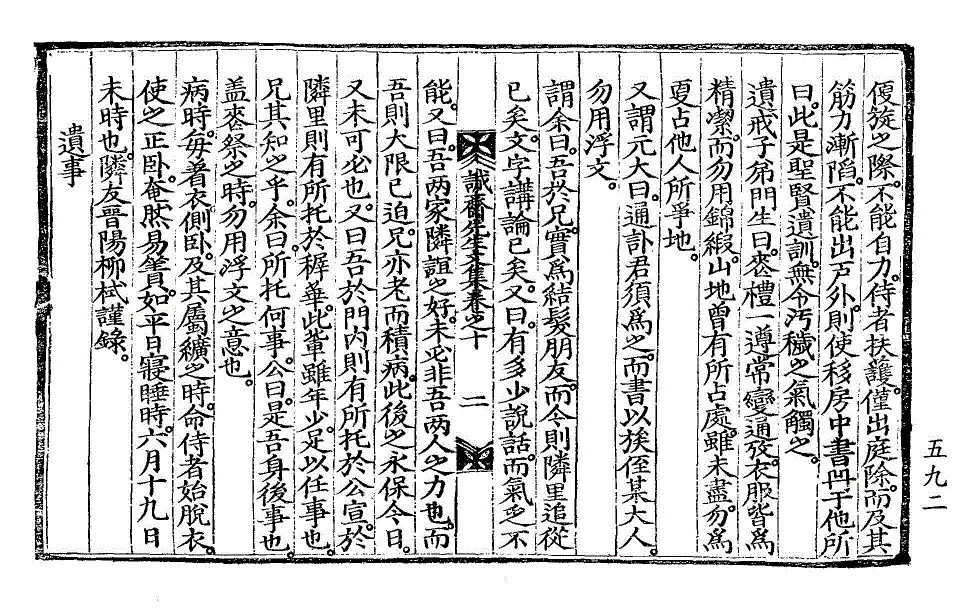 便旋之际。不能自力。侍者扶护。仅出庭除。而及其筋力渐陷。不能出户外。则使移房中书册于他所曰。此是圣贤遗训。无令污秽之气触之。
便旋之际。不能自力。侍者扶护。仅出庭除。而及其筋力渐陷。不能出户外。则使移房中书册于他所曰。此是圣贤遗训。无令污秽之气触之。遗戒子弟门生曰。丧礼一遵常变通考。衣服皆为精洁。而勿用锦缎。山地曾有所占处。虽未尽。勿为更占他人所争地。
又谓元大曰。通讣君须为之。而书以族侄某大人。勿用浮文。
谓余曰。吾于兄。实为结发朋友。而今则邻里追从已矣。文字讲论已矣。又曰。有多少说话。而气乏不能。又曰。吾两家邻谊之好。未必非吾两人之力也。而吾则大限已迫。兄亦老而积病。此后之永保今日。又未可必也。又曰吾于门内则有所托于公宣。于邻里则有所托于稚华。此辈虽年少。足以任事也。兄其知之乎。余曰。所托何事。公曰。是吾身后事也。盖丧祭之时。勿用浮文之意也。
病时。每着衣侧卧。及其属纩之时。命侍者始脱衣。使之正卧。奄然易箦。如平日寝睡时。六月十九日未时也。邻友晋阳柳栻谨录。
遗事[柳栻]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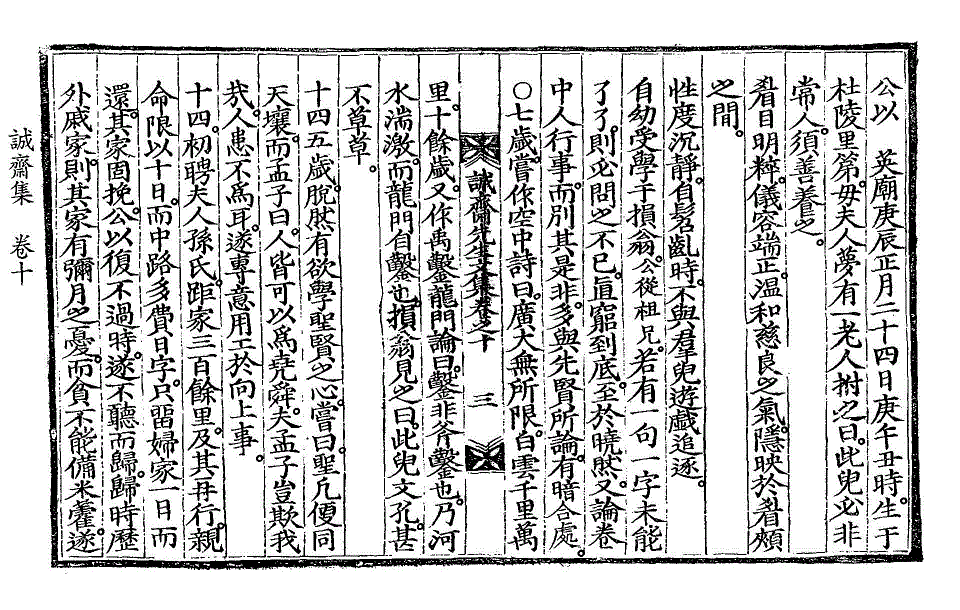 公以 英庙庚辰正月二十四日庚午丑时。生于杜陵里第。母夫人梦有一老人拊之曰。此儿必非常人。须善养之。
公以 英庙庚辰正月二十四日庚午丑时。生于杜陵里第。母夫人梦有一老人拊之曰。此儿必非常人。须善养之。眉目明粹。仪容端正。温和慈良之气。隐映于眉颊之间。
性度沉静。自髫龀时。不与群儿游戏追逐。
自幼受学于损翁。(公从祖兄。)若有一句一字未能了了。则必问之不已。直穷到底。至于晓然。又论卷中人行事。而别其是非。多与先贤所论。有暗合处。
○七岁。尝作空中诗曰。广大无所限。白云千里万里。十馀岁。又作禹凿龙门论曰。凿非斧凿也。乃河水湍激。而龙门自凿也。损翁见之曰。此儿文孔。甚不草草。
十四五岁。脱然有欲学圣贤之心。尝曰。圣凡便同天壤。而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夫孟子岂欺我哉。人患不为耳。遂专意用工于向上事。
十四。初聘夫人孙氏。距家三百馀里。及其再行。亲命限以十日。而中路多费日字。只留妇家一日而还。其家固挽。公以复不过时。遂不听而归。归时历外戚家。则其家有弥月之忧。而贫不能备米藿。遂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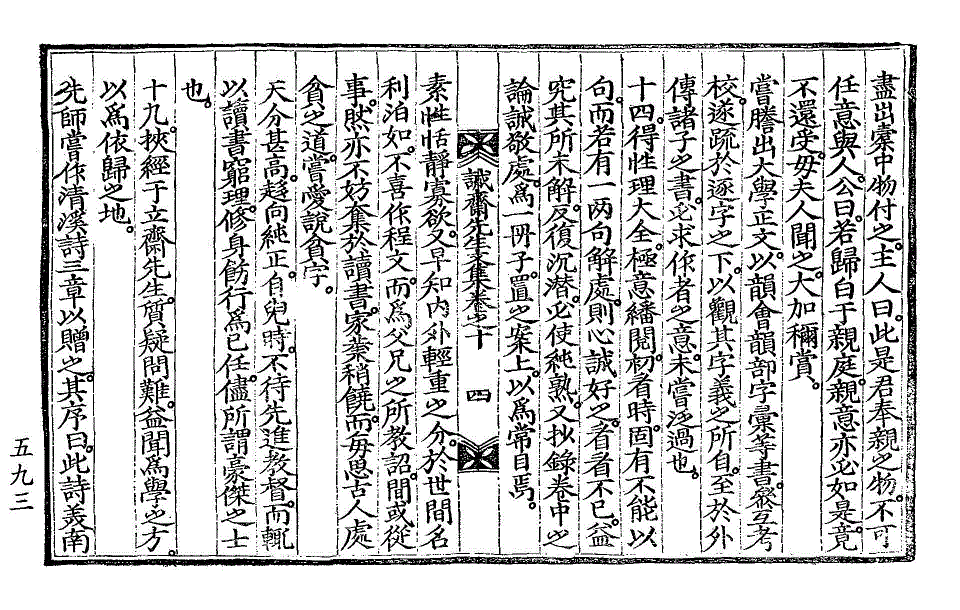 尽出橐中物付之。主人曰。此是君奉亲之物。不可任意与人。公曰。若归白于亲庭。亲意亦必如是。竟不还受。母夫人闻之。大加称赏。
尽出橐中物付之。主人曰。此是君奉亲之物。不可任意与人。公曰。若归白于亲庭。亲意亦必如是。竟不还受。母夫人闻之。大加称赏。尝誊出大学正文。以韵会韵部字汇等书。参互考校。遂疏于逐字之下。以观其字义之所自。至于外传诸子之书。必求作者之意。未尝泛过也。
十四。得性理大全。极意翻阅。初看时。固有不能以句。而若有一两句解处。则心诚好之。看看不已。益究其所未解。反复沉潜。必使纯熟。又抄录卷中之论诚敬处。为一册子。置之案上。以为常目焉。
素性恬静寡欲。又早知内外轻重之分。于世间名利泊如。不喜作程文。而为父兄之所教诏。间或从事。然亦不妨夺于读书。家业稍饶。而每思古人处贫之道。尝爱说贫字。
天分甚高。趍向纯正。自儿时。不待先进教督。而辄以读书穷理。修身饬行为己任。尽所谓豪杰之士也。
十九。挟经于立斋先生。质疑问难。益闻为学之方。以为依归之地。
先师尝作清溪诗三章以赠之。其序曰。此诗美南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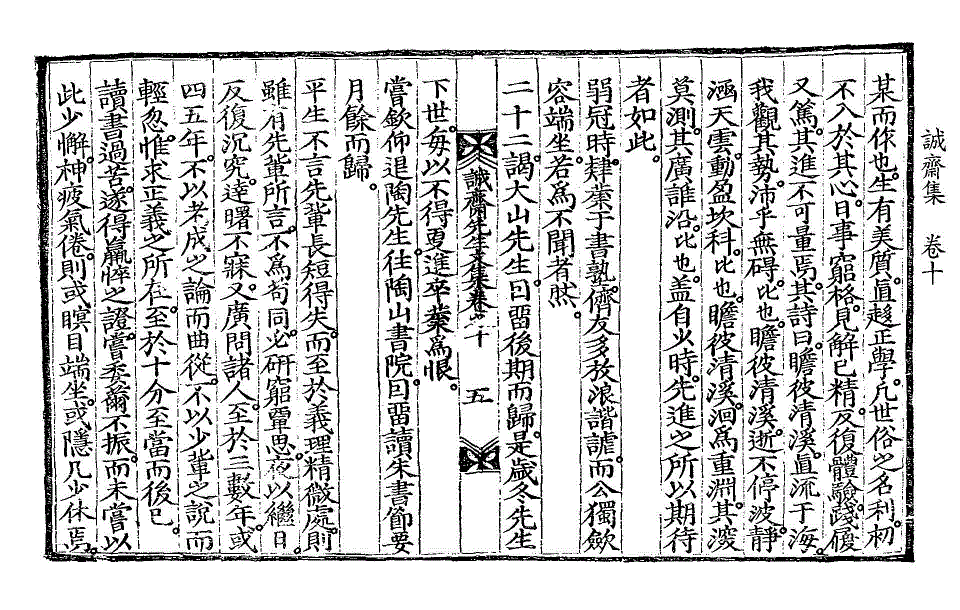 某而作也。生有美质。直趍正学。凡世俗之名利。初不入于其心。日事穷格。见解已精。反复体验。践履又笃。其进不可量焉。其诗曰。瞻彼清溪。直流于海。我观其势。沛乎无碍。(比也。)瞻彼清溪。逝不停波。静涵天云。动盈坎科。(比也。)瞻彼清溪。洄为重渊。其深莫测。其广谁沿。(比也。)盖自少时。先进之所以期待者如此。
某而作也。生有美质。直趍正学。凡世俗之名利。初不入于其心。日事穷格。见解已精。反复体验。践履又笃。其进不可量焉。其诗曰。瞻彼清溪。直流于海。我观其势。沛乎无碍。(比也。)瞻彼清溪。逝不停波。静涵天云。动盈坎科。(比也。)瞻彼清溪。洄为重渊。其深莫测。其广谁沿。(比也。)盖自少时。先进之所以期待者如此。弱冠时。肄业于书塾。侪友多放浪谐谑。而公独敛容端坐。若为不闻者然。
二十二。谒大山先生。因留后期而归。是岁冬先生下世。每以不得更进卒业为恨。
尝钦仰退陶先生。往陶山书院。因留读朱书节要月馀而归。
平生不言先辈长短得失。而至于义理精微处。则虽有先辈所言。不为苟同。必研穷覃思。夜以继日。反复沉究。达曙不寐。又广问诸人。至于三数年。或四五年。不以老成之论而曲从。不以少辈之说而轻忽。惟求正义之所在。至于十分至当而后已。
读书过苦。遂得羸悴之證。尝委薾不振。而未尝以此少懈。神疲气倦。则或瞑目端坐。或隐几少休焉。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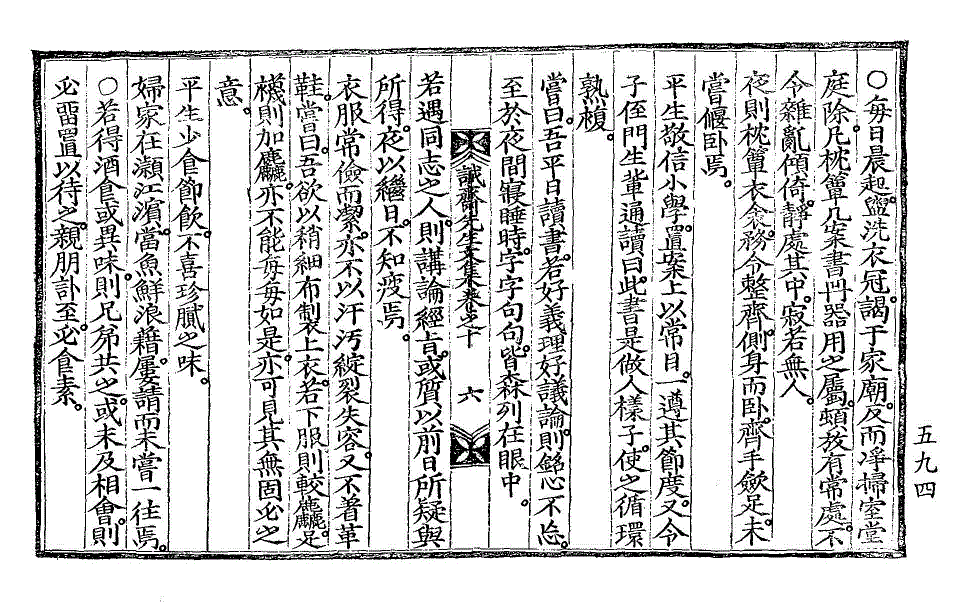 ○每日晨起。盥洗衣冠。谒于家庙。反而净扫室堂庭除。凡枕簟几案书册器用之属。顿放有常处。不令杂乱倾倚。静处其中。寂若无人。
○每日晨起。盥洗衣冠。谒于家庙。反而净扫室堂庭除。凡枕簟几案书册器用之属。顿放有常处。不令杂乱倾倚。静处其中。寂若无人。夜则枕簟衣衾。务令整齐。侧身而卧。齐手敛足。未尝偃卧焉。
平生敬信小学。置案上以常目。一遵其节度。又令子侄门生辈通读曰。此书是做人样子。使之循环熟复。
尝曰。吾平日读书。若好义理好议论。则铭心不忘。至于夜间寝睡时。字字句句。皆森列在眼中。
若遇同志之人。则讲论经旨。或质以前日所疑与所得。夜以继日。不知疲焉。
衣服常俭而洁。亦不以汗污绽裂失容。又不着革鞋。尝曰。吾欲以稍细布制上衣。若下服则较粗。足袜则加粗。亦不能每每如是。亦可见其无固必之意。
平生少食节饮。不喜珍腻之味。
妇家在𤃡江滨。当鱼鲜浪藉。屡请而未尝一往焉。
○若得酒食或异味。则兄弟共之。或未及相会。则必留置以待之。亲朋讣至。必食素。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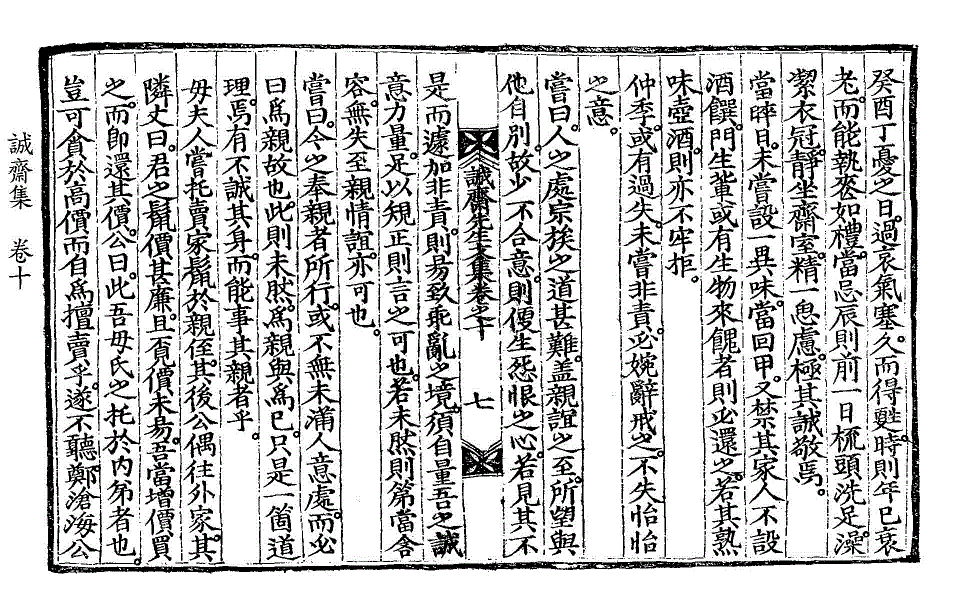 癸酉丁忧之日。过哀气塞。久而得苏。时则年已衰老。而能执丧如礼。当忌辰则前一日梳头洗足。澡洁衣冠。静坐斋室。精一思虑。极其诚敬焉。
癸酉丁忧之日。过哀气塞。久而得苏。时则年已衰老。而能执丧如礼。当忌辰则前一日梳头洗足。澡洁衣冠。静坐斋室。精一思虑。极其诚敬焉。当晬日。未尝设一异味。当回甲。又禁其家人不设酒馔。门生辈或有生物来馈者则必还之。若其熟味壶酒。则亦不牢拒。
仲季。或有过失。未尝非责。必婉辞戒之。不失怡怡之意。
尝曰。人之处宗族之道甚难。盖亲谊之至。所望与他自别。故少不合意。则便生怨恨之心。若见其不是而遽加非责。则易致乖乱之境。须自量吾之诚意力量。足以规正则言之可也。若未然则第当含容。无失至亲情谊。亦可也。
尝曰。今之奉亲者所行。或不无未满人意处。而必曰为亲故也。此则未然。为亲与为己。只是一个道理。焉有不诚其身。而能事其亲者乎。
母夫人尝托卖家鬣于亲侄。其后公偶往外家。其邻丈曰。君之鬣价甚廉。且觅价未易。吾当增价买之。而即还其价。公曰。此吾母氏之托于内弟者也。岂可贪于高价而自为擅卖乎。遂不听。郑沧海公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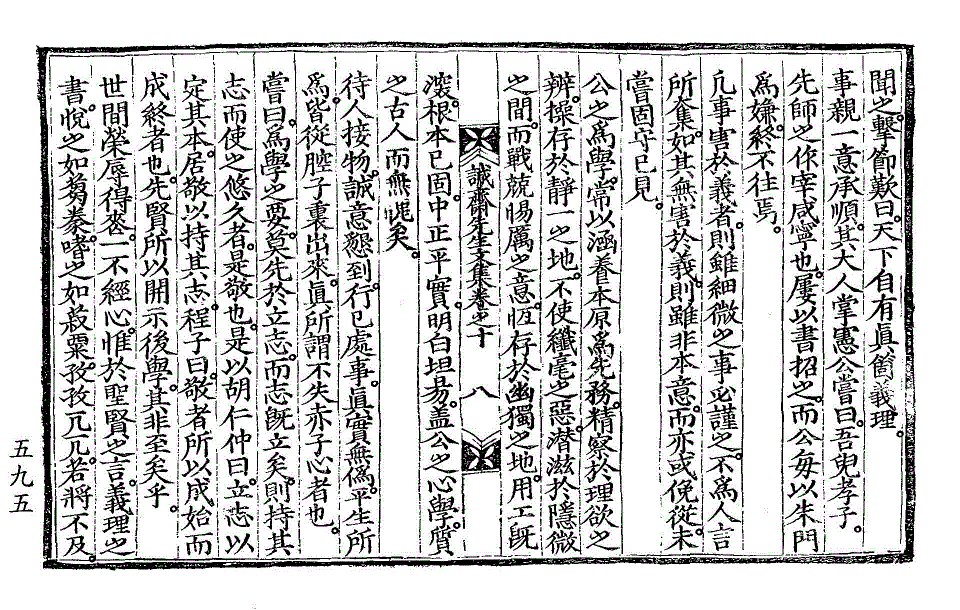 闻之。击节叹曰。天下自有真个义理。
闻之。击节叹曰。天下自有真个义理。事亲一意承顺。其大人掌宪公尝曰。吾儿孝子。
先师之作宰咸宁也。屡以书招之。而公每以朱门为嫌。终不往焉。
凡事害于义者。则虽细微之事必谨之。不为人言所夺。如其无害于义。则虽非本意。而亦或俛从。未尝固守己见。
公之为学。常以涵养本原为先务。精察于理欲之辨。操存于静一之地。不使纤毫之恶。潜滋于隐微之间。而战兢惕厉之意。恒存于幽独之地。用工既深。根本已固。中正平实。明白坦易。盖公之心学。质之古人而无愧矣。
待人接物。诚意恳到。行己处事。真实无伪。平生所为。皆从腔子里出来。真所谓不失赤子心者也。
尝曰。为学之要。莫先于立志。而志既立矣。则持其志而使之悠久者。是敬也。是以胡仁仲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程子曰。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先贤所以开示后学。其非至矣乎。
世间荣辱得丧。一不经心。惟于圣贤之言。义理之书。悦之如刍豢。嗜之如菽粟。孜孜兀兀。若将不及。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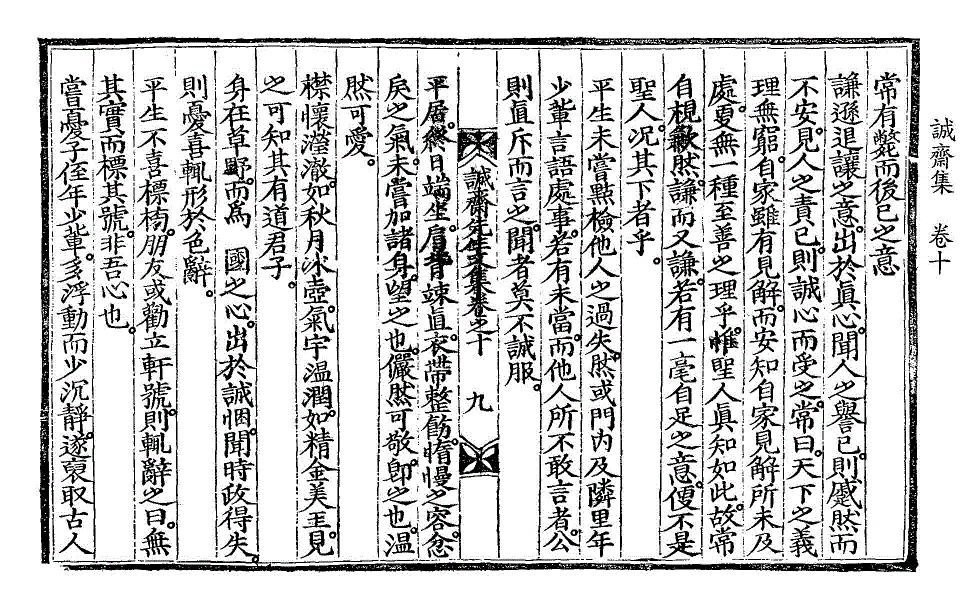 常有毙而后已之意
常有毙而后已之意谦逊退让之意。出于真心。闻人之誉己。则蹙然而不安。见人之责己。则诚心而受之。常曰。天下之义理无穷。自家虽有见解。而安知自家见解所未及处。更无一种至善之理乎。惟圣人真知如此。故常自视歉然。谦而又谦。若有一毫自足之意。便不是圣人。况其下者乎。
平生未尝点检他人之过失。然或门内及邻里年少辈言语处事。若有未当。而他人所不敢言者。公则直斥而言之。闻者莫不诚服。
平居。终日端坐。肩背竦直。衣带整饬。惰慢之容。忿戾之气。未尝加诸身。望之也。俨然可敬。即之也。温然可爱。
襟怀滢澈。如秋月冰壶。气宇温润。如精金美玉。见之可知其有道君子。
身在草野。而为 国之心。出于诚悃。闻时政得失。则忧喜辄形于色辞。
平生不喜标榜。朋友或劝立轩号。则辄辞之曰。无其实而标其号。非吾心也。
尝忧子侄年少辈。多浮动而少沉静。遂裒取古人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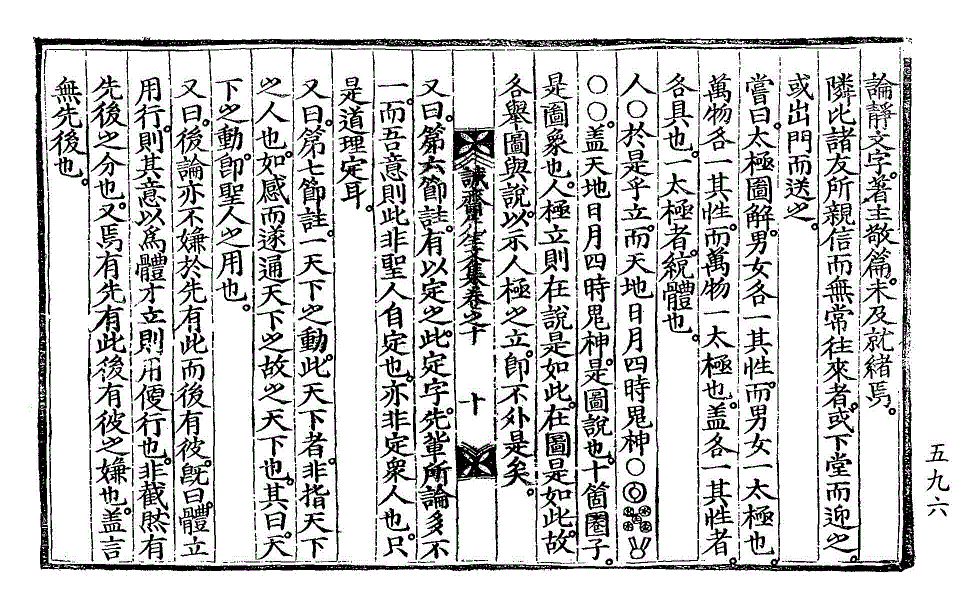 论静文字。著主敬篇。未及就绪焉。
论静文字。著主敬篇。未及就绪焉。邻比诸友所亲信而无常往来者。或下堂而迎之。或出门而送之。
尝曰。太极图解。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各一其性者。各具也。一太极者。统体也。
人
又曰。第六节注。有以定之。此定字。先辈所论多不一。而吾意则此非圣人自定也。亦非定众人也。只是道理定耳。
又曰。第七节注。一天下之动。此天下者。非指天下之人也。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天下也。其曰。天下之动。即圣人之用也。
又曰。后论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既曰。体立用行。则其意以为体才立则用便行也。非截然有先后之分也。又焉有先有此后有彼之嫌也。盖言无先后也。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7H 页
 天命之性。是就气质中指其大本也。以大本之性。谓有偏全者。诚若可骇。然天之赋物也。固非片片分而与之。而气有偏全。理亦不得不有偏全也。况是性也。乃仁义礼智之性也。若以物性皆具仁义礼智。则其于率性之道。说不去矣。
天命之性。是就气质中指其大本也。以大本之性。谓有偏全者。诚若可骇。然天之赋物也。固非片片分而与之。而气有偏全。理亦不得不有偏全也。况是性也。乃仁义礼智之性也。若以物性皆具仁义礼智。则其于率性之道。说不去矣。戒慎恐惧之所以兼动静者。以其自所睹所闻。以至于不睹不闻也。故就此一节而论之。则是兼动静。对下文慎独而言。则慎独是动也。不睹不闻是静也。子希以为虽对下文慎独而言。上文之兼动静。依旧自在也。公以为不然。
心之所以兼理气者。以其统性也。若分开说。则性是理也。心可属之气一边也。子希以为虽分开说。心之兼理气自若也。公以为不然。
中庸或问。自不睹不闻之前。或以为不睹不闻之前。则是睹闻时也。恐未然也。古人于当用时字处用前字。故生时谓之生前。如李白诗所谓且乐生前一杯酒之类是也。据此则不睹不闻之前。即不睹不闻之时也。如是看之。方与下文谨独相对。
先辈论不睹不闻。而引蟋蟀诗。职思其外当之曰。既思其闻见所及。而又至于不见不闻处也。此可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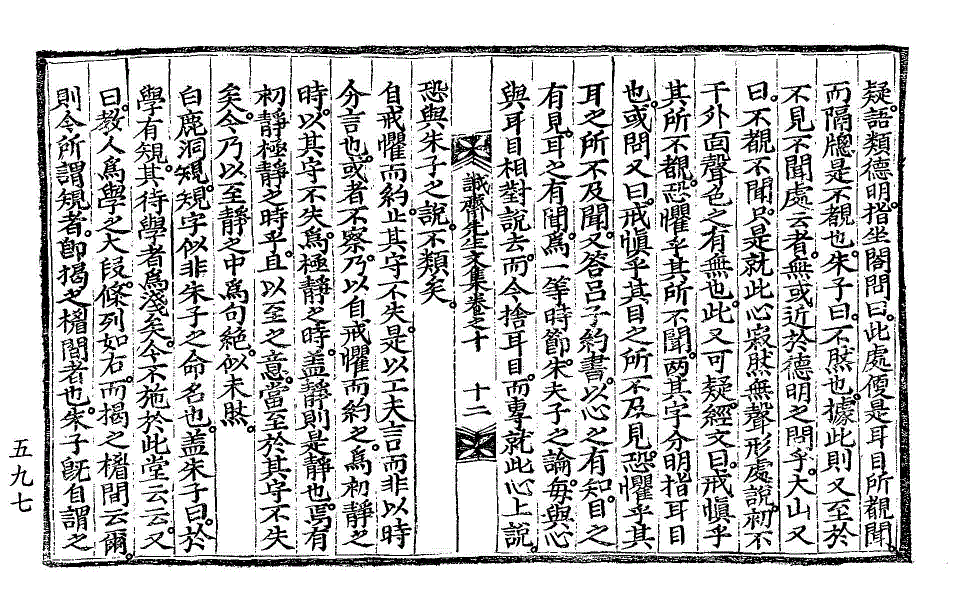 疑。语类德明。指坐閤问曰。此处便是耳目所睹闻。而隔窗是不睹也。朱子曰。不然也。据此则又至于不见不闻处云者。无或近于德明之问乎。大山又曰。不睹不闻。只是就此心寂然无声形处说。初不干外面声色之有无也。此又可疑。经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两其字分明指耳目也。或问又曰。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见。恐惧乎其耳之所不及闻。又答吕子约书。以心之有知。目之有见。耳之有闻。为一等时节。朱夫子之论。每与心与耳目相对说去。而今舍耳目。而专就此心上说。恐与朱子之说。不类矣。
疑。语类德明。指坐閤问曰。此处便是耳目所睹闻。而隔窗是不睹也。朱子曰。不然也。据此则又至于不见不闻处云者。无或近于德明之问乎。大山又曰。不睹不闻。只是就此心寂然无声形处说。初不干外面声色之有无也。此又可疑。经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两其字分明指耳目也。或问又曰。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见。恐惧乎其耳之所不及闻。又答吕子约书。以心之有知。目之有见。耳之有闻。为一等时节。朱夫子之论。每与心与耳目相对说去。而今舍耳目。而专就此心上说。恐与朱子之说。不类矣。自戒惧而约。(止)其守不失。是以工夫言而非以时分言也。或者不察。乃以自戒惧而约之。为初静之时。以其守不失。为极静之时。盖静则是静也。焉有初静极静之时乎。且以至之意。当至于其守不失矣。今乃以至静之中为句绝。似未然。
白鹿洞规。规字似非朱子之命名也。盖朱子曰。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浅矣。今不施于此堂云云。又曰。教人为学之大段。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云尔。则今所谓规者。即揭之楣间者也。朱子既自谓之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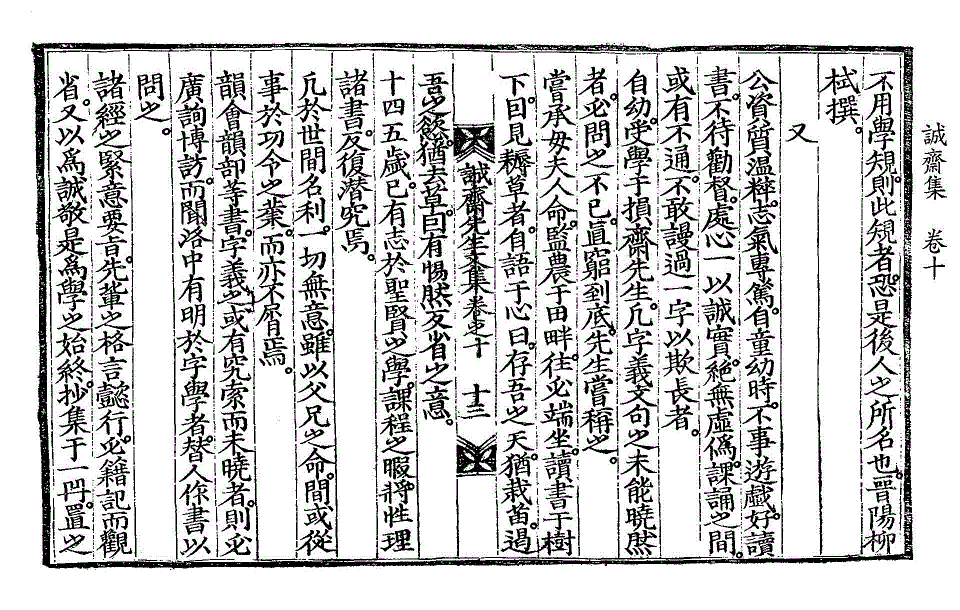 不用学规。则此规者。恐是后人之所名也。晋阳柳栻撰。
不用学规。则此规者。恐是后人之所名也。晋阳柳栻撰。遗事[南汉普]
公资质温粹。志气专笃。自童幼时。不事游戏。好读书。不待劝督。处心一以诚实。绝无虚伪。课诵之间。或有不通。不敢谩过一字以欺长者。
自幼。受学于损斋先生。凡字义文句之未能晓然者。必问之不已。直穷到底。先生尝称之。
尝承母夫人命。监农于田畔。往必端坐。读书于树下。因见耨草者。自语于心曰。存吾之天。犹栽苗。遏吾之欲。犹去草。因有惕然反省之意。
十四五岁。已有志于圣贤之学。课程之暇。将性理诸书。反复潜究焉。
凡于世间名利。一切无意。虽以父兄之命。间或从事于功令之业。而亦不屑焉。
韵会韵部等书。字义之或有究索而未晓者。则必广询博访。而闻洛中有明于字学者。替人作书以问之。
诸经之紧意要旨。先辈之格言懿行。必籍记而观省。又以为诚敬是为学之始终。抄集于一册。置之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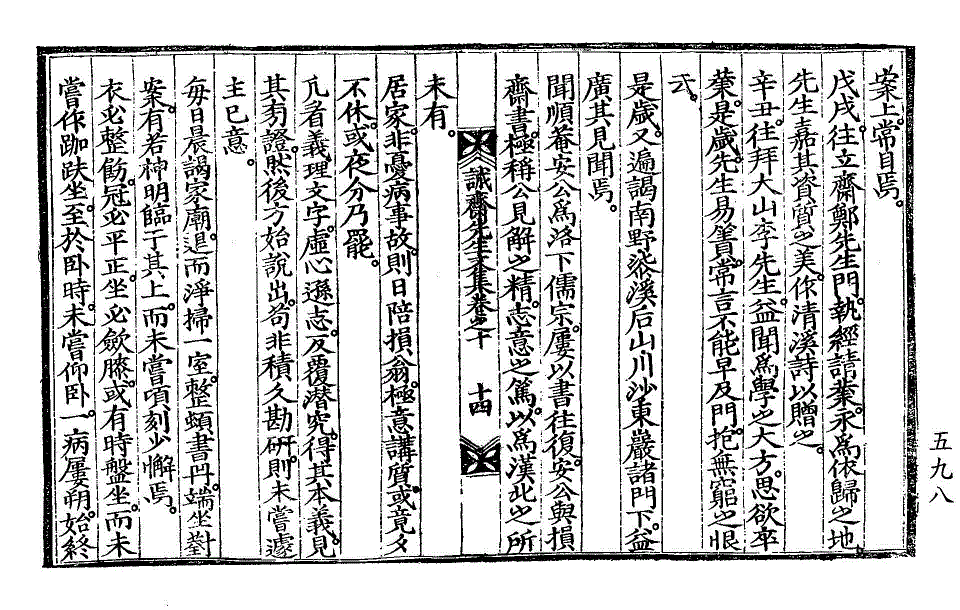 案上。常目焉。
案上。常目焉。戊戌。往立斋郑先生门。执经请业。永为依归之地。先生嘉其资质之美。作清溪诗以赠之。
辛丑。往拜大山李先生。益闻为学之大方。思欲卒业。是岁。先生易箦。常言不能早及门。抱无穷之恨云。
是岁。又遍谒南野,漆溪,后山,川沙,东岩诸门下。益广其见闻焉。
闻顺庵安公为洛下儒宗。屡以书往复。安公与损斋书。极称公见解之精。志意之笃。以为汉北之所未有。
居家。非忧病事故。则日陪损翁。极意讲质。或竟夕不休。或夜分乃罢。
凡看义理文字。虚心逊志。反覆潜究。得其本义。见其旁證。然后方始说出。苟非积久勘研。则未尝遽主己意。
每日晨谒家庙。退而净扫一室。整顿书册。端坐对案。有若神明临于其上。而未尝顷刻少懈焉。
衣必整饬。冠必平正。坐必敛膝。或有时盘坐。而未尝作跏趺坐。至于卧时。未尝仰卧。一病屡朔。始终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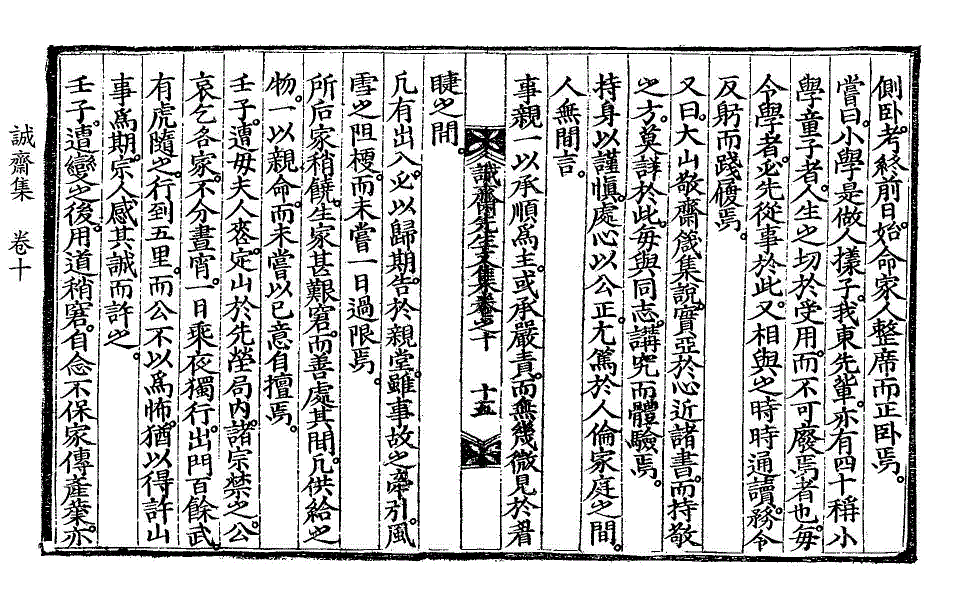 侧卧。考终前日。始命家人整席而正卧焉。
侧卧。考终前日。始命家人整席而正卧焉。尝曰。小学是做人㨾子。我东先辈。亦有四十称小学童子者。人生之切于受用。而不可废焉者也。每令学者。必先从事于此。又相与之时时通读。务令反躬而践履焉。
又曰。大山敬斋箴集说。实亚于心近诸书。而持敬之方。莫详于此。每与同志。讲究而体验焉。
持身以谨慎。处心以公正。尤笃于人伦家庭之间。人无间言。
事亲一以承顺为主。或承严责。而无几微见于眉睫之间。
凡有出入。必以归期。告于亲堂。虽事故之牵引。风雪之阻梗。而未尝一日过限焉。
所后家稍饶。生家甚艰窘。而善处其间。凡供给之物。一以亲命。而未尝以己意自擅焉。
壬子。遭母夫人丧。定山于先茔局内。诸宗禁之。公哀乞各家。不分昼宵。一日乘夜独行。出门百馀武。有虎随之。行到五里。而公不以为怖。犹以得许山事为期。宗人感其诚而许之。
壬子。遭变之后。用道稍窘。自念不保家传产业。亦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599L 页
 非人子之职。遂检敕农作。撙节财用。数年之后。稍有赢馀。旋思人子之继先无忝。有大于此者。且贫富有命。不可役役于此。遂不复为意。
非人子之职。遂检敕农作。撙节财用。数年之后。稍有赢馀。旋思人子之继先无忝。有大于此者。且贫富有命。不可役役于此。遂不复为意。仲弟汉醇。尝以难名之證。出没死生。公昼夜扶护。不解衣就寝者。殆数月。汤药饮食。必亲自省检。而未尝委诸傍人。
本生侄艗正早失慈。即收养于家。至长成而拊爱教育。若己子焉。
壬戌七月。诸友作既望会于𤃡江。公亦来会。济胜诸具已陈。忽自寤曰。吾辈以 先王化育中物。而 国哀才毕。招朋结队。作此游赏之乐。有不安于心。遂罢会。
癸卯。赴宜宁试。距试所半日程。而同行有病。以看护无人。遂停初场焉。
甲子。有事端于道院。左右以事关师门。不可噤默。劝其发文。公以为作文分疏。有非尊卫之道。终始持重。四面之责。纷然日至。而终不变所守焉。
屏虎之论起而一道波荡。远近纷纭。虽有一定之见。而每隐忧于心。未尝以姓名出之门外。乃于绍院治疏之日。作书于疏首。以为尊贤卫道。自有道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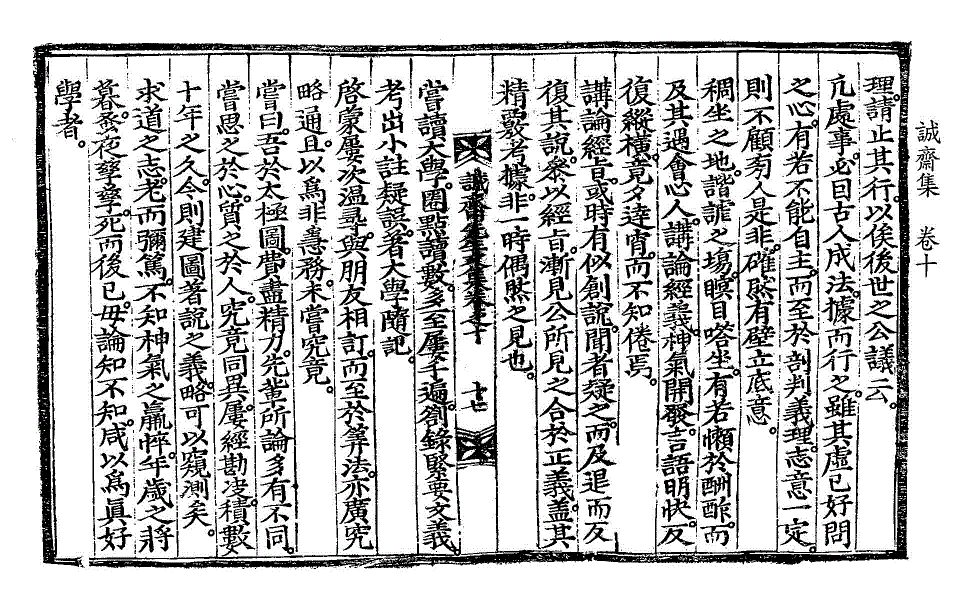 理。请止其行。以俟后世之公议云。
理。请止其行。以俟后世之公议云。凡处事。必因古人成法。据而行之。虽其虚己好问之心。有若不能自主。而至于剖判义理。志意一定。则不顾旁人是非。确然有壁立底意。
稠坐之地。谐谑之场。瞑目㗳坐。有若懒于酬酢。而及其遇会心人。讲论经义。神气开发。言语明快。反复纵横。竟夕达宵。而不知倦焉。
讲论经旨。或时有似创说。闻者疑之。而及退而反复其说。参以经旨。渐见公所见之合于正义。盖其精覈考据。非一时偶然之见也。
尝读大学。圈点读数。多至屡千遍。劄录紧要文义。考出小注疑误。著大学随记。
启蒙屡次温寻。与朋友相订。而至于算法。亦广究略通。且以为非急务。未尝究竟。
尝曰。吾于太极图。费尽精力。先辈所论多有不同。尝思之于心。质之于人。究竟同异。屡经勘决。积数十年之久。今则建图著说之义。略可以窥测矣。
求道之志。老而弥笃。不知神气之羸悴。年岁之将暮。蚤夜孳孳。死而后已。毋论知不知。咸以为真好学者。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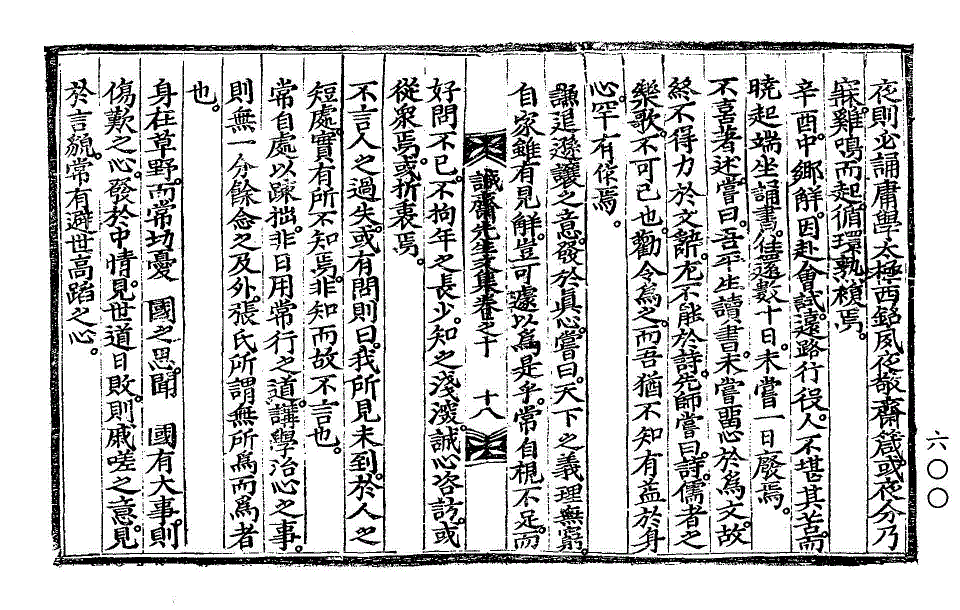 夜则必诵庸学,太极,西铭,夙夜,敬斋箴。或夜分乃寐。鸡鸣而起。循环熟复焉。
夜则必诵庸学,太极,西铭,夙夜,敬斋箴。或夜分乃寐。鸡鸣而起。循环熟复焉。辛酉。中乡解。因赴会试。远路行役。人不堪其苦。而晓起端坐诵书。往还数十日。未尝一日废焉。
不喜著述。尝曰。吾平生读书。未尝留心于为文。故终不得力于文辞。尤不能于诗。先师尝曰。诗。儒者之乐歌。不可已也。劝令为之。而吾犹不知有益于身心。罕有作焉。
谦退逊让之意。发于真心。尝曰。天下之义理无穷。自家虽有见解。岂可遽以为是乎。常自视不足。而好问不已。不拘年之长少。知之浅深。诚心咨访。或从众焉。或折衷焉。
不言人之过失。或有问则曰。我所见未到。于人之短处。实有所不知焉。非知而故不言也。
常自处以疏拙。非日用常行之道。讲学治心之事。则无一分馀念之及外。张氏所谓无所为而为者也。
身在草野。而常切忧 国之思。闻 国有大事。则伤叹之心。发于中情。见世道日败。则戚嗟之意。见于言貌。常有避世高蹈之心。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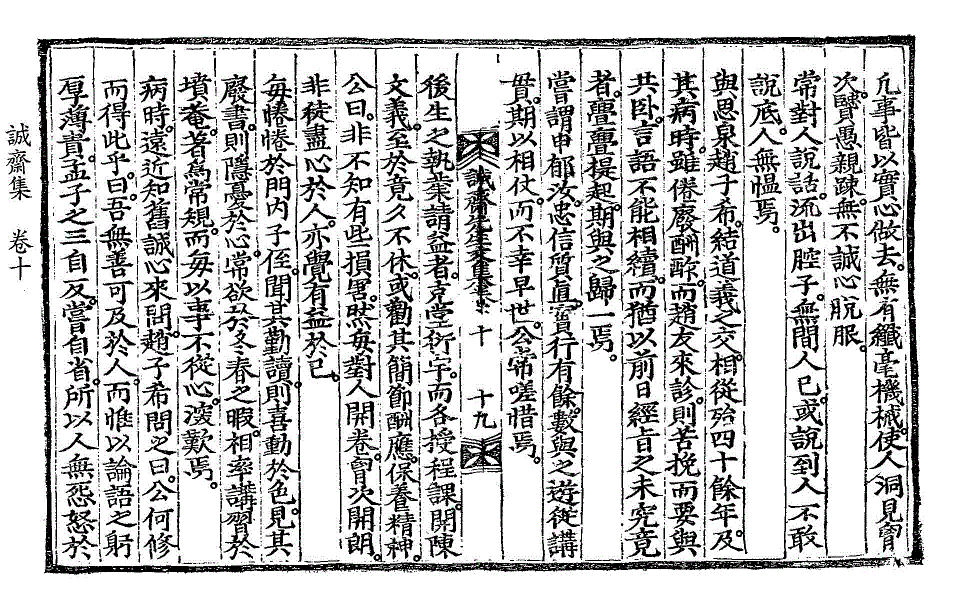 凡事皆以实心做去。无有纤毫机械。使人洞见胸次。贤愚亲疏。无不诚心脱服。
凡事皆以实心做去。无有纤毫机械。使人洞见胸次。贤愚亲疏。无不诚心脱服。常对人说话。流出腔子。无间人己。或说到人不敢说底。人无愠焉。
与思泉赵子希。结道义之交。相从殆四十馀年。及其病时。虽倦废酬酢。而赵友来诊。则苦挽而要与共卧。言语不能相续。而犹以前日经旨之未究竟者。亹亹提起。期与之归一焉。
尝谓申郁汝。忠信质直。实行有馀。数与之游从讲贯。期以相仗。而不幸早世。公常嗟惜焉。
后生之执业请益者。克堂衍宇。而各授程课。开陈文义。至于竟夕不休。或劝其简节酬应。保养精神。公曰。非不知有些损害。然每对人开卷。胸次开朗。非徒尽心于人。亦觉有益于己。
每惓惓于门内子侄。闻其勤读。则喜动于色。见其废书。则隐忧于心。常欲于冬春之暇。相率讲习于坟庵。著为常规。而每以事不从心。深叹焉。
病时。远近知旧诚心来问。赵子希问之曰。公何修而得此乎。曰。吾无善可及于人。而惟以论语之躬厚薄责。孟子之三自反。尝自省。所以人无怨怒于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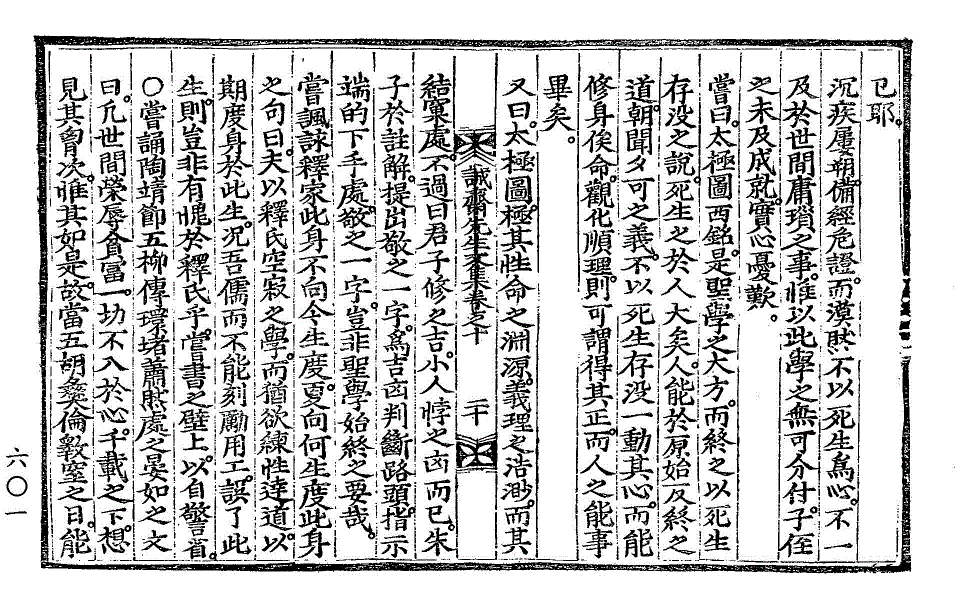 己耶。
己耶。沉疾屡朔。备经危證。而漠然不以死生为心。不一及于世间庸琐之事。惟以此学之无可分付。子侄之未及成就。实心忧叹。
尝曰。太极图西铭。是圣学之大方。而终之以死生存没之说。死生之于人大矣。人能于原始反终之道。朝闻夕可之义。不以死生存没一动其心。而能修身俟命。观化顺理。则可谓得其正。而人之能事毕矣。
又曰。太极图。极其性命之渊源。义理之浩渺。而其结窠处。不过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已。朱子于注解。提出敬之一字。为吉凶判断路头。指示端的下手处。敬之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哉。
尝讽咏释家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之句曰。夫以释氏空寂之学。而犹欲练性达道。以期度身于此生。况吾儒而不能刻励用工。误了此生。则岂非有愧于释氏乎。尝书之壁上。以自警省。
○尝诵陶靖节五柳传环堵萧然处之晏如之文曰。凡世间荣辱贫富。一切不入于心。千载之下。想见其胸次。惟其如是。故当五胡彝伦斁窒之日。能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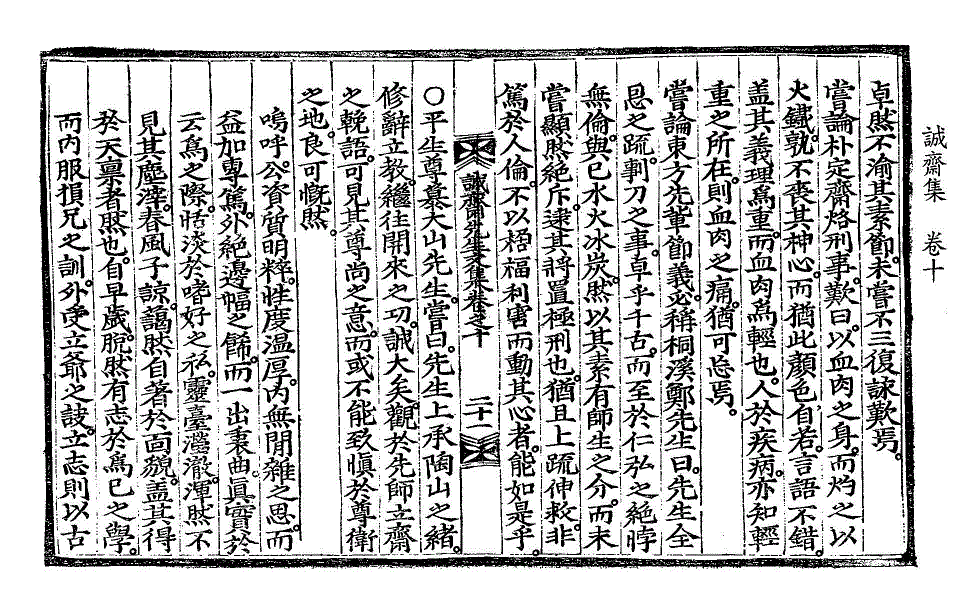 卓然不渝其素节。未尝不三复咏叹焉。
卓然不渝其素节。未尝不三复咏叹焉。尝论朴定斋烙刑事。叹曰。以血肉之身。而灼之以火铁。孰不丧其神心。而犹此颜色自若。言语不错。盖其义理为重。而血肉为轻也。人于疾病。亦知轻重之所在。则血肉之痛。犹可忘焉。
尝论东方先辈节义。必称桐溪郑先生曰。先生全恩之疏。剚刀之事。卓乎千古。而至于仁弘之绝悖无伦。与己水火冰炭。然以其素有师生之分。而未尝显然绝斥。逮其将置极刑也。犹且上疏伸救。非笃于人伦。不以祸福利害而动其心者。能如是乎。
○平生尊慕大山先生。尝曰。先生上承陶山之绪。修辞立教。继往开来之功。诚大矣。观于先师立斋之挽语。可见其尊尚之意。而或不能致慎于尊卫之地。良可慨然。
呜呼。公资质明粹。性度温厚。内无閒杂之思。而益加专笃。外绝边幅之饰。而一出衷曲。真实于云为之际。恬淡于嗜好之私。灵台滢澈。浑然不见其尘滓。春风子谅。蔼然自著于面貌。盖其得于天禀者然也。自早岁。脱然有志于为己之学。而内服损兄之训。外受立爷之诀。立志则以古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2L 页
 人自期。读书则以穷理为本。惕励之志。无间于隐显。究索之功。不懈于造次。义理之精。则不使有毫发之差。用心之微。则不容隐纤芥之恶。自视不足而谦谦焉虚己。好问是勤。而恳恳乎取人。俛焉孜孜。死而后已。好学之诚。求道之志。盖已真切而笃实矣。是以诚敬交至。行解俱到。孝悌之人无间言。德义之日用相须。操履之笃于内而守之坚确。忠信之及于外而推之溥博。道理之浃洽于身心。符验之睟盎于面背。贤愚亲疏。诚心说服。咸以为有道君子。盖其心法一直做去。自动及静。由表彻里。只有纯实而都无虚伪。故所以学造乎精深。行质于神明。邹夫子所谓不失赤子之心者。非公之谓欤。公尝自谦而无标号。公之友思泉赵子希。用私谥之例。号之曰诚斋。庶乎得公之心矣。乃者哀胤以我有门内从游之久。勤托遗事。顾以知德甚难。不敢遽然承当。而旋自念汉普自童幼时从公游。今到白首矣。猥以为相知之深。有在于族亲之外。而终无一言之记述。则与不知公者。无以异矣。略摭平日所闻见为一录。而宁使之略。不敢为溢
人自期。读书则以穷理为本。惕励之志。无间于隐显。究索之功。不懈于造次。义理之精。则不使有毫发之差。用心之微。则不容隐纤芥之恶。自视不足而谦谦焉虚己。好问是勤。而恳恳乎取人。俛焉孜孜。死而后已。好学之诚。求道之志。盖已真切而笃实矣。是以诚敬交至。行解俱到。孝悌之人无间言。德义之日用相须。操履之笃于内而守之坚确。忠信之及于外而推之溥博。道理之浃洽于身心。符验之睟盎于面背。贤愚亲疏。诚心说服。咸以为有道君子。盖其心法一直做去。自动及静。由表彻里。只有纯实而都无虚伪。故所以学造乎精深。行质于神明。邹夫子所谓不失赤子之心者。非公之谓欤。公尝自谦而无标号。公之友思泉赵子希。用私谥之例。号之曰诚斋。庶乎得公之心矣。乃者哀胤以我有门内从游之久。勤托遗事。顾以知德甚难。不敢遽然承当。而旋自念汉普自童幼时从公游。今到白首矣。猥以为相知之深。有在于族亲之外。而终无一言之记述。则与不知公者。无以异矣。略摭平日所闻见为一录。而宁使之略。不敢为溢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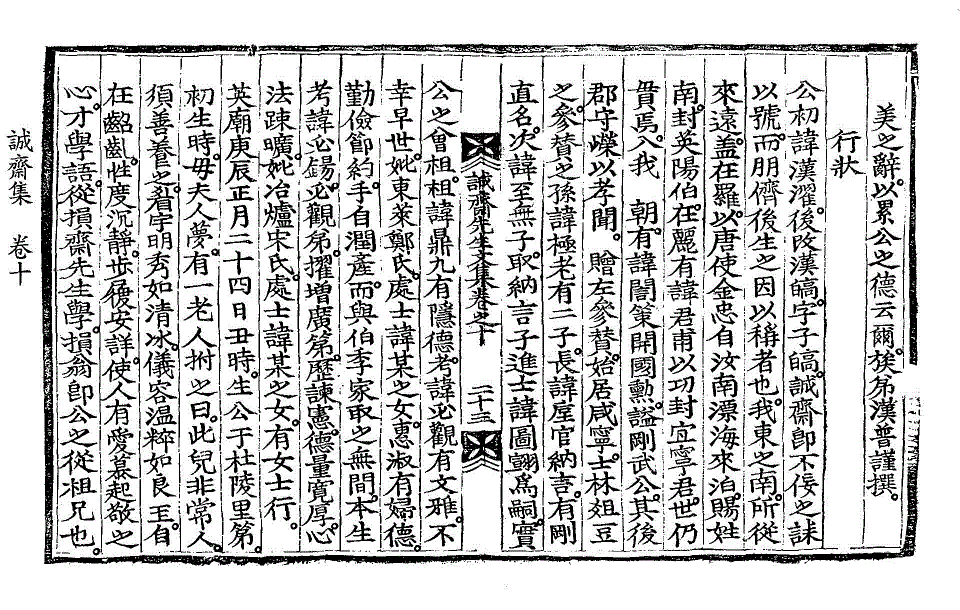 美之辞。以累公之德云尔。族弟汉普谨撰。
美之辞。以累公之德云尔。族弟汉普谨撰。行状[赵承洙]
公初讳汉濯。后改汉皓。字子皓。诚斋即不佞之诔以号。而朋侪后生之因以称者也。我东之南。所从来远。盖在罗。以唐使金忠自汝南漂海来泊。赐姓南。封英阳伯。在丽有讳君甫以功封宜宁君。世仍贯焉。入我 朝。有讳訚策开国勋。谥刚武公。其后郡守嵘以孝闻。 赠左参赞。始居咸宁。士林俎豆之。参赞之孙讳极老有二子。长讳垕官纳言。有刚直名。次讳至无子。取纳言子进士讳图翧为嗣。实公之曾祖。祖讳鼎九有隐德。考讳必观有文雅。不幸早世。妣东莱郑氏。处士讳某之女。惠淑有妇德。勤俭节约。手自润产。而与伯季家取之无间。本生考讳必锡。必观弟。擢增广第。历谏宪。德量宽厚。心法疏旷。妣冶炉宋氏。处士讳某之女。有女士行。 英庙庚辰正月二十四日丑时。生公于杜陵里第。初生时。母夫人梦。有一老人拊之曰。此儿非常人。须善养之。眉宇明秀如清冰。仪容温粹如良玉。自在龆龀。性度沉静。步履安详。使人有爱慕起敬之心。才学语。从损斋先生学。损翁即公之从祖兄也。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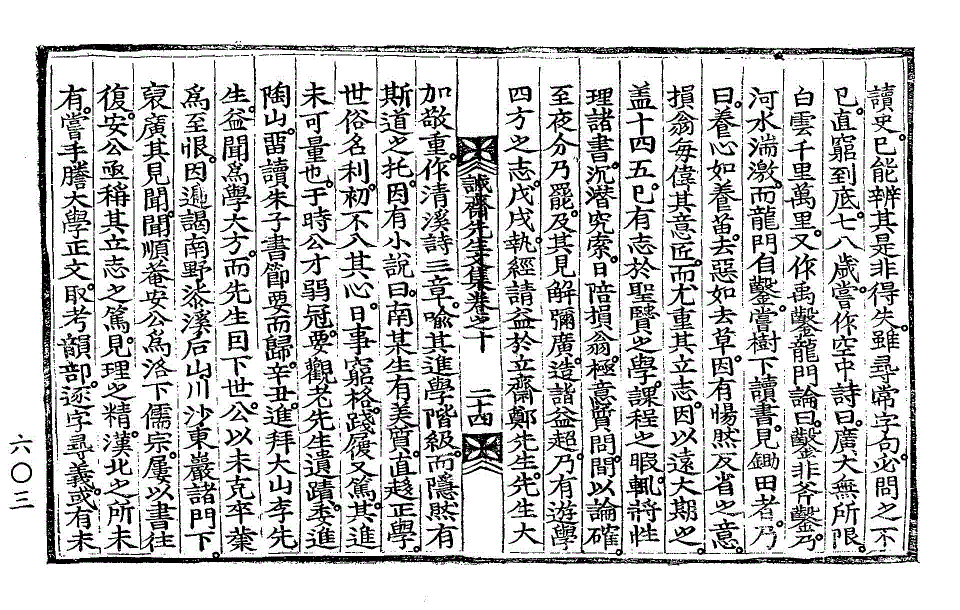 读史。已能辨其是非得失。虽寻常字句。必问之不已。直穷到底。七八岁。尝作空中诗曰。广大无所限。白云千里万里。又作禹凿龙门论曰。凿非斧凿。乃河水湍激。而龙门自凿。尝树下读书。见锄田者。乃曰。养心如养苗。去恶如去草。因有惕然反省之意。损翁每伟其意匠。而尤重其立志。因以远大期之。盖十四五。已有志于圣贤之学。课程之暇。辄将性理诸书。沉潜究索。日陪损翁。极意质问。间以论确。至夜分乃罢。及其见解弥广。造诣益超。乃有游学四方之志。戊戌。执经请益于立斋郑先生。先生大加敬重。作清溪诗三章。喻其进学阶级。而隐然有斯道之托。因有小说曰。南某生有美质。直趍正学。世俗名利。初不入其心。日事穷格。践履又笃。其进未可量也。于时公才弱冠。要观老先生遗迹。委进陶山。留读朱子书节要而归。辛丑。进拜大山李先生。益闻为学大方。而先生因下世。公以未克卒业为至恨。因遍谒南野,漆溪,后山,川沙,东岩诸门下。裒广其见闻。闻顺庵安公为洛下儒宗。屡以书往复。安公亟称其立志之笃。见理之精。汉北之所未有。尝手誊大学正文。取考韵部。逐字寻义。或有未
读史。已能辨其是非得失。虽寻常字句。必问之不已。直穷到底。七八岁。尝作空中诗曰。广大无所限。白云千里万里。又作禹凿龙门论曰。凿非斧凿。乃河水湍激。而龙门自凿。尝树下读书。见锄田者。乃曰。养心如养苗。去恶如去草。因有惕然反省之意。损翁每伟其意匠。而尤重其立志。因以远大期之。盖十四五。已有志于圣贤之学。课程之暇。辄将性理诸书。沉潜究索。日陪损翁。极意质问。间以论确。至夜分乃罢。及其见解弥广。造诣益超。乃有游学四方之志。戊戌。执经请益于立斋郑先生。先生大加敬重。作清溪诗三章。喻其进学阶级。而隐然有斯道之托。因有小说曰。南某生有美质。直趍正学。世俗名利。初不入其心。日事穷格。践履又笃。其进未可量也。于时公才弱冠。要观老先生遗迹。委进陶山。留读朱子书节要而归。辛丑。进拜大山李先生。益闻为学大方。而先生因下世。公以未克卒业为至恨。因遍谒南野,漆溪,后山,川沙,东岩诸门下。裒广其见闻。闻顺庵安公为洛下儒宗。屡以书往复。安公亟称其立志之笃。见理之精。汉北之所未有。尝手誊大学正文。取考韵部。逐字寻义。或有未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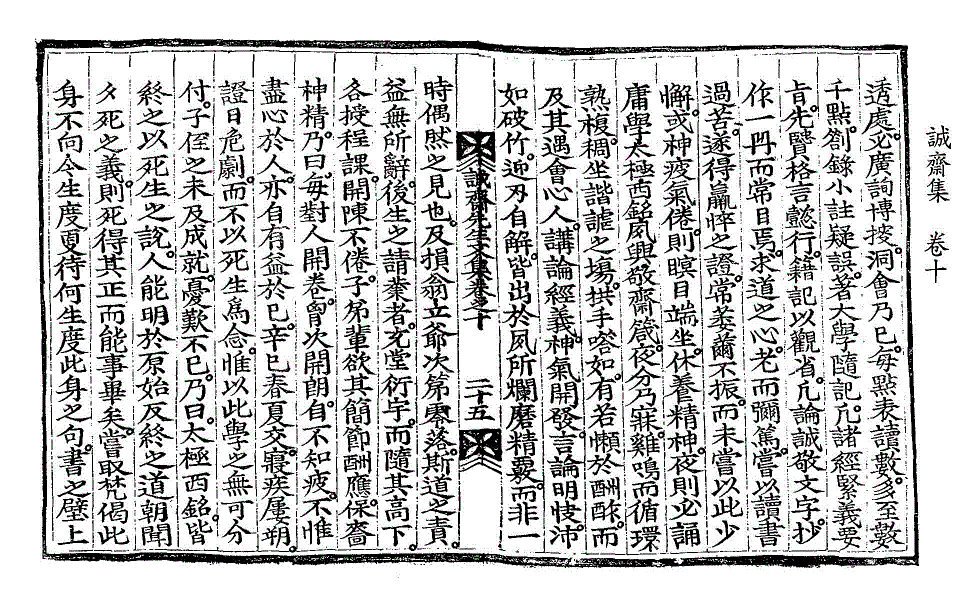 透处。必广询博搜。洞会乃已。每点表读数。多至数千点。劄录小注疑误。著大学随记。凡诸经紧义要旨。先贤格言懿行。籍记以观省。凡论诚敬文字。抄作一册而常目焉。求道之心。老而弥笃。尝以读书过苦。遂得羸悴之證。常萎薾不振。而未尝以此少懈。或神疲气倦。则瞑目端坐。休养精神。夜则必诵庸学,太极,西铭,夙兴,敬斋箴。夜分乃寐。鸡鸣而循环熟复。稠坐谐谑之场。拱手㗳如。有若懒于酬酢。而及其遇会心人。讲论经义。神气开发。言论明快。沛如破竹。迎刃自解。皆出于夙所烂磨精覈。而非一时偶然之见也。及损翁,立爷次第零落。斯道之责。益无所辞。后生之请业者。充堂衍宇。而随其高下。各授程课。开陈不倦。子弟辈欲其简节酬应。保啬神精。乃曰。每对人开卷。胸次开朗。自不知疲。不惟尽心于人。亦自有益于己。辛巳春夏交。寝疾屡朔。證日危剧。而不以死生为念。惟以此学之无可分付。子侄之未及成就。忧叹不已。乃曰。太极西铭。皆终之以死生之说。人能明于原始反终之道朝闻夕死之义。则死得其正而能事毕矣。尝取梵偈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之句。书之壁上
透处。必广询博搜。洞会乃已。每点表读数。多至数千点。劄录小注疑误。著大学随记。凡诸经紧义要旨。先贤格言懿行。籍记以观省。凡论诚敬文字。抄作一册而常目焉。求道之心。老而弥笃。尝以读书过苦。遂得羸悴之證。常萎薾不振。而未尝以此少懈。或神疲气倦。则瞑目端坐。休养精神。夜则必诵庸学,太极,西铭,夙兴,敬斋箴。夜分乃寐。鸡鸣而循环熟复。稠坐谐谑之场。拱手㗳如。有若懒于酬酢。而及其遇会心人。讲论经义。神气开发。言论明快。沛如破竹。迎刃自解。皆出于夙所烂磨精覈。而非一时偶然之见也。及损翁,立爷次第零落。斯道之责。益无所辞。后生之请业者。充堂衍宇。而随其高下。各授程课。开陈不倦。子弟辈欲其简节酬应。保啬神精。乃曰。每对人开卷。胸次开朗。自不知疲。不惟尽心于人。亦自有益于己。辛巳春夏交。寝疾屡朔。證日危剧。而不以死生为念。惟以此学之无可分付。子侄之未及成就。忧叹不已。乃曰。太极西铭。皆终之以死生之说。人能明于原始反终之道朝闻夕死之义。则死得其正而能事毕矣。尝取梵偈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之句。书之壁上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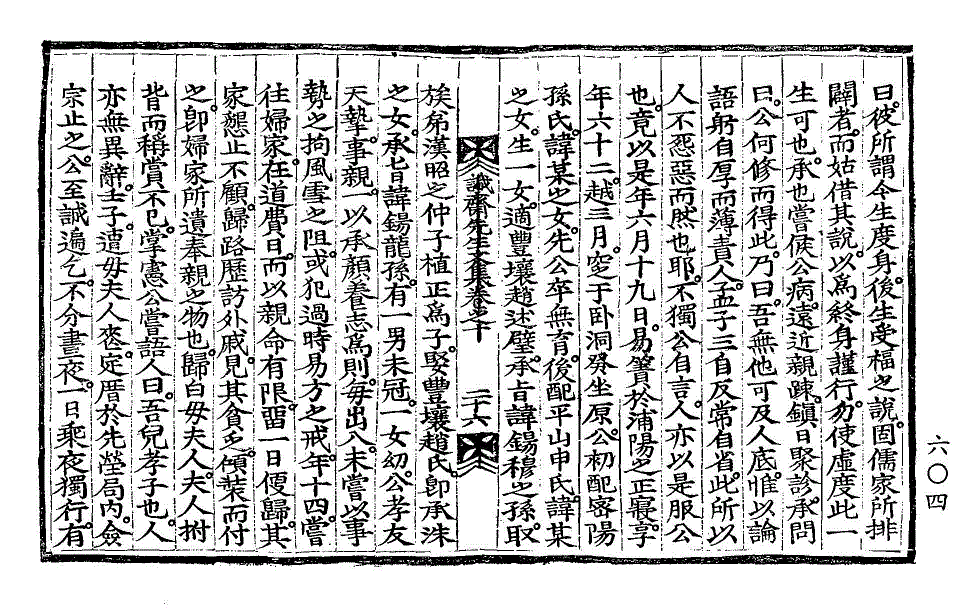 曰。彼所谓今生度身。后生受福之说。固儒家所排辟者。而姑借其说。以为终身谨行。勿使虚度此一生可也。承也尝候公病。远近亲疏。镇日聚诊。承问曰。公何修而得此。乃曰。吾无他可及人底。惟以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人。孟子三自反常自省。此所以人不怨恶而然也耶。不独公自言。人亦以是服公也。竟以是年六月十九日。易箦于浦阳之正寝。享年六十二。越三月。窆于卧洞癸坐原。公初配密阳孙氏。讳某之女。先公卒无育。后配平山申氏。讳某之女。生一女。适丰壤赵述璧。承旨讳锡穆之孙。取族弟汉昭之仲子植正为子。娶丰壤赵氏。即承洙之女。承旨讳锡龙孙。有一男未冠。一女幼。公孝友天挚。事亲。一以承颜养志为则。每出入。未尝以事势之拘风雪之阻。或犯过时易方之戒。年十四。尝往妇家。在道费日。而以亲命有限。留一日便归。其家恳止不顾。归路历访外戚。见其贫乏。倾装而付之。即妇家所遗奉亲之物也。归白母夫人。夫人拊背而称赏不已。掌宪公尝语人曰。吾儿孝子也。人亦无异辞。壬子。遭母夫人丧。定厝于先茔局内。佥宗止之。公至诚遍乞。不分昼夜。一日乘夜独行。有
曰。彼所谓今生度身。后生受福之说。固儒家所排辟者。而姑借其说。以为终身谨行。勿使虚度此一生可也。承也尝候公病。远近亲疏。镇日聚诊。承问曰。公何修而得此。乃曰。吾无他可及人底。惟以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人。孟子三自反常自省。此所以人不怨恶而然也耶。不独公自言。人亦以是服公也。竟以是年六月十九日。易箦于浦阳之正寝。享年六十二。越三月。窆于卧洞癸坐原。公初配密阳孙氏。讳某之女。先公卒无育。后配平山申氏。讳某之女。生一女。适丰壤赵述璧。承旨讳锡穆之孙。取族弟汉昭之仲子植正为子。娶丰壤赵氏。即承洙之女。承旨讳锡龙孙。有一男未冠。一女幼。公孝友天挚。事亲。一以承颜养志为则。每出入。未尝以事势之拘风雪之阻。或犯过时易方之戒。年十四。尝往妇家。在道费日。而以亲命有限。留一日便归。其家恳止不顾。归路历访外戚。见其贫乏。倾装而付之。即妇家所遗奉亲之物也。归白母夫人。夫人拊背而称赏不已。掌宪公尝语人曰。吾儿孝子也。人亦无异辞。壬子。遭母夫人丧。定厝于先茔局内。佥宗止之。公至诚遍乞。不分昼夜。一日乘夜独行。有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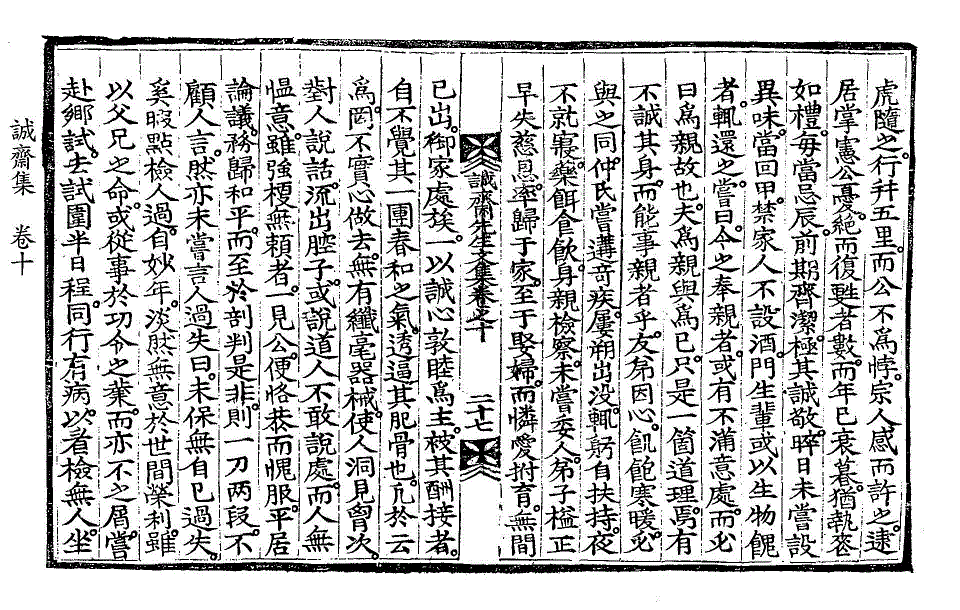 虎随之。行并五里。而公不为悖。宗人感而许之。逮居掌宪公忧。绝而复苏者数。而年已衰暮。犹执丧如礼。每当忌辰。前期齐洁。极其诚敬。晬日未尝设异味。当回甲。禁家人不设酒。门生辈或以生物馈者。辄还之。尝曰。今之奉亲者。或有不满意处。而必曰为亲故也。夫为亲与为己。只是一个道理。焉有不诚其身。而能事亲者乎。友弟因心。饥饱寒暖。必与之同。仲氏尝遘奇疾。屡朔出没。辄躬自扶持。夜不就寝。药饵食饮。身亲检察。未尝委人。弟子艗正早失慈恩。率归于家。至于娶妇。而怜爱拊育。无间己出。御家处族。一以诚心敦睦为主。被其酬接者。自不觉其一团春和之气。透逼其肌骨也。凡于云为。罔不实心做去。无有纤毫器械。使人洞见胸次。对人说话。流出腔子。或说道人不敢说处。而人无愠意。虽强梗无赖者。一见公。便恪恭而愧服。平居论议。务归和平。而至于剖判是非。则一刀两段。不顾人言。然亦未尝言人过失曰。未保无自己过失。奚暇点检人过。自妙年。淡然无意于世间荣利。虽以父兄之命。或从事于功令之业。而亦不之屑。尝赴乡试。去试围半日程。同行有病。以看检无人。坐
虎随之。行并五里。而公不为悖。宗人感而许之。逮居掌宪公忧。绝而复苏者数。而年已衰暮。犹执丧如礼。每当忌辰。前期齐洁。极其诚敬。晬日未尝设异味。当回甲。禁家人不设酒。门生辈或以生物馈者。辄还之。尝曰。今之奉亲者。或有不满意处。而必曰为亲故也。夫为亲与为己。只是一个道理。焉有不诚其身。而能事亲者乎。友弟因心。饥饱寒暖。必与之同。仲氏尝遘奇疾。屡朔出没。辄躬自扶持。夜不就寝。药饵食饮。身亲检察。未尝委人。弟子艗正早失慈恩。率归于家。至于娶妇。而怜爱拊育。无间己出。御家处族。一以诚心敦睦为主。被其酬接者。自不觉其一团春和之气。透逼其肌骨也。凡于云为。罔不实心做去。无有纤毫器械。使人洞见胸次。对人说话。流出腔子。或说道人不敢说处。而人无愠意。虽强梗无赖者。一见公。便恪恭而愧服。平居论议。务归和平。而至于剖判是非。则一刀两段。不顾人言。然亦未尝言人过失曰。未保无自己过失。奚暇点检人过。自妙年。淡然无意于世间荣利。虽以父兄之命。或从事于功令之业。而亦不之屑。尝赴乡试。去试围半日程。同行有病。以看检无人。坐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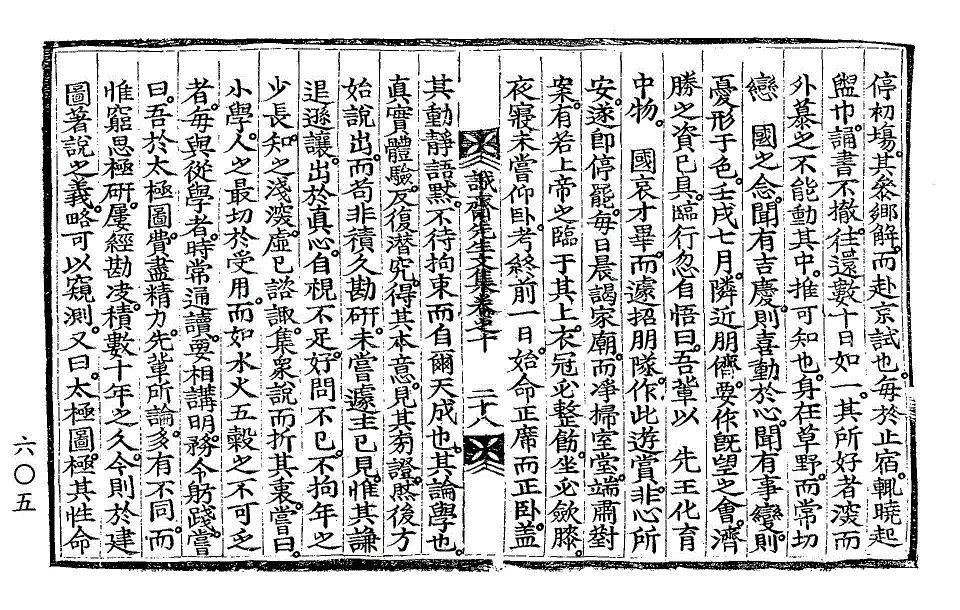 停初场。其参乡解。而赴京试也。每于止宿。辄晓起盥巾。诵书不撤。往还数十日如一。其所好者深而外慕之不能动其中。推可知也。身在草野。而常切恋 国之念。闻有吉庆。则喜动于心。闻有事变。则忧形于色。壬戌七月。邻近朋侪。要作既望之会。济胜之资已具。临行忽自悟曰。吾辈以 先王化育中物。 国哀才毕。而遽招朋队。作此游赏。非心所安。遂即停罢。每日晨谒家庙。而净扫室堂。端肃对案。有若上帝之临于其上。衣冠必整饬。坐必敛膝。夜寝未尝仰卧。考终前一日。始命正席而正卧。盖其动静语默。不待拘束而自尔天成也。其论学也。真实体验。反复潜究。得其本意。见其旁證。然后方始说出。而苟非积久勘研。未尝遽主己见。惟其谦退逊让。出于真心。自视不足。好问不已。不拘年之少长。知之浅深。虚己咨诹。集众说而折其衷。尝曰。小学。人之最切于受用。而如水火五谷之不可乏者。每与从学者。时常通读。要相讲明。务令躬践。尝曰。吾于太极图。费尽精力。先辈所论。多有不同。而惟穷思极研。屡经勘决。积数十年之久。今则于建图著说之义。略可以窥测。又曰。太极图。极其性命
停初场。其参乡解。而赴京试也。每于止宿。辄晓起盥巾。诵书不撤。往还数十日如一。其所好者深而外慕之不能动其中。推可知也。身在草野。而常切恋 国之念。闻有吉庆。则喜动于心。闻有事变。则忧形于色。壬戌七月。邻近朋侪。要作既望之会。济胜之资已具。临行忽自悟曰。吾辈以 先王化育中物。 国哀才毕。而遽招朋队。作此游赏。非心所安。遂即停罢。每日晨谒家庙。而净扫室堂。端肃对案。有若上帝之临于其上。衣冠必整饬。坐必敛膝。夜寝未尝仰卧。考终前一日。始命正席而正卧。盖其动静语默。不待拘束而自尔天成也。其论学也。真实体验。反复潜究。得其本意。见其旁證。然后方始说出。而苟非积久勘研。未尝遽主己见。惟其谦退逊让。出于真心。自视不足。好问不已。不拘年之少长。知之浅深。虚己咨诹。集众说而折其衷。尝曰。小学。人之最切于受用。而如水火五谷之不可乏者。每与从学者。时常通读。要相讲明。务令躬践。尝曰。吾于太极图。费尽精力。先辈所论。多有不同。而惟穷思极研。屡经勘决。积数十年之久。今则于建图著说之义。略可以窥测。又曰。太极图。极其性命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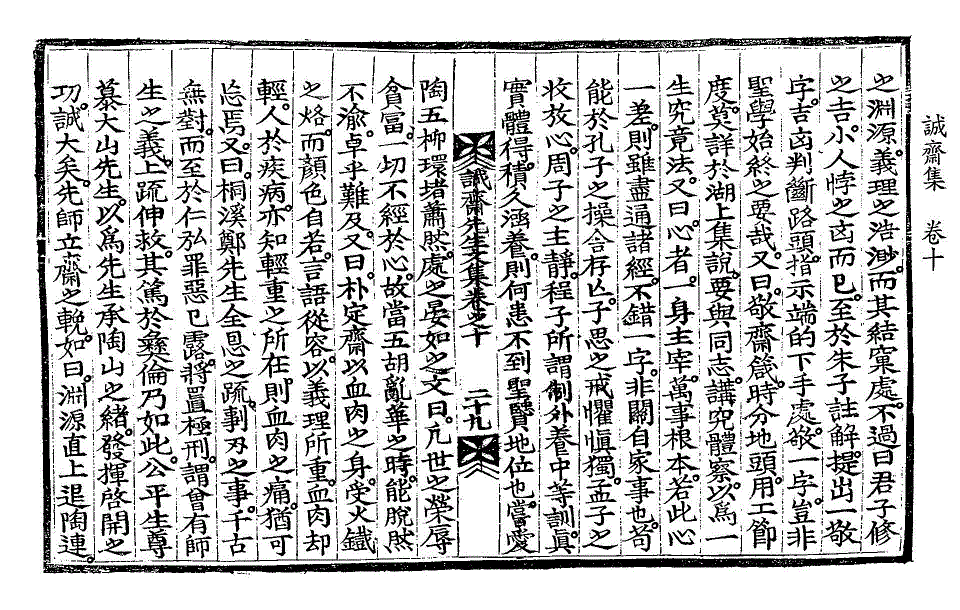 之渊源。义理之浩渺。而其结窠处。不过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已。至于朱子注解。提出一敬字。吉凶判断路头。指示端的下手处。敬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哉。又曰。敬斋箴。时分地头。用工节度。莫详于湖上集说。要与同志。讲究体察。以为一生究竟法。又曰。心者。一身主宰。万事根本。若此心一差。则虽尽通诸经。不错一字。非关自家事也。苟能于孔子之操舍存亡。子思之戒惧慎独。孟子之收放心。周子之主静。程子所谓制外养中等训。真实体得。积久涵养。则何患不到圣贤地位也。尝爱陶五柳环堵萧然。处之晏如之文曰。凡世之荣辱贫富。一切不经于心。故当五胡乱华之时。能脱然不渝。卓乎难及。又曰。朴定斋以血肉之身。受火铁之烙。而颜色自若。言语从容。以义理所重。血肉却轻。人于疾病。亦知轻重之所在。则血肉之痛。犹可忘焉。又曰。桐溪郑先生全恩之疏。剚刃之事。千古无对。而至于仁弘罪恶已露。将置极刑。谓曾有师生之义。上疏伸救。其笃于彝伦乃如此。公平生尊慕大山先生。以为先生承陶山之绪。发挥启开之功。诚大矣。先师立斋之挽。如曰。渊源直上退陶连。
之渊源。义理之浩渺。而其结窠处。不过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已。至于朱子注解。提出一敬字。吉凶判断路头。指示端的下手处。敬一字。岂非圣学始终之要哉。又曰。敬斋箴。时分地头。用工节度。莫详于湖上集说。要与同志。讲究体察。以为一生究竟法。又曰。心者。一身主宰。万事根本。若此心一差。则虽尽通诸经。不错一字。非关自家事也。苟能于孔子之操舍存亡。子思之戒惧慎独。孟子之收放心。周子之主静。程子所谓制外养中等训。真实体得。积久涵养。则何患不到圣贤地位也。尝爱陶五柳环堵萧然。处之晏如之文曰。凡世之荣辱贫富。一切不经于心。故当五胡乱华之时。能脱然不渝。卓乎难及。又曰。朴定斋以血肉之身。受火铁之烙。而颜色自若。言语从容。以义理所重。血肉却轻。人于疾病。亦知轻重之所在。则血肉之痛。犹可忘焉。又曰。桐溪郑先生全恩之疏。剚刃之事。千古无对。而至于仁弘罪恶已露。将置极刑。谓曾有师生之义。上疏伸救。其笃于彝伦乃如此。公平生尊慕大山先生。以为先生承陶山之绪。发挥启开之功。诚大矣。先师立斋之挽。如曰。渊源直上退陶连。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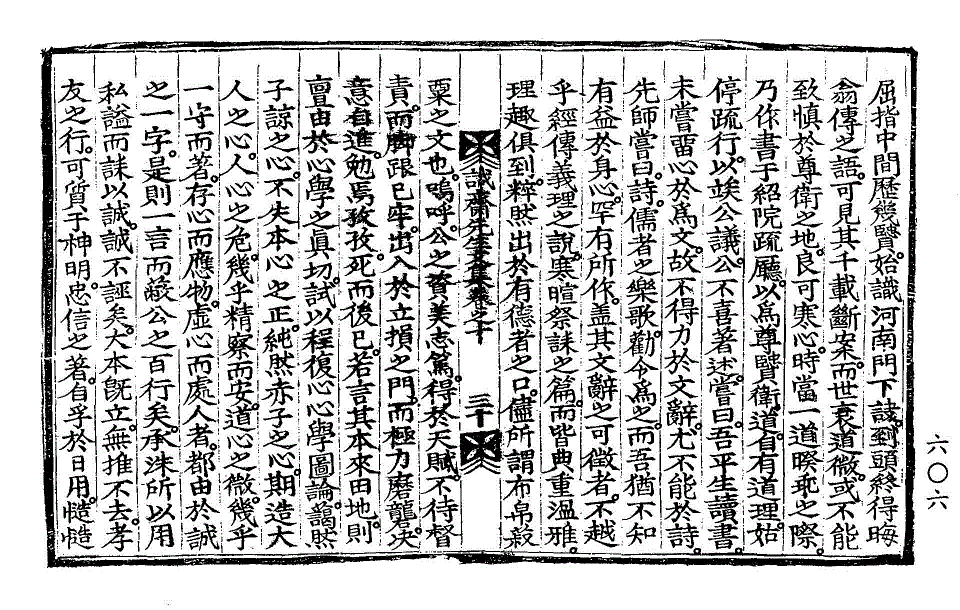 屈指中间历几贤。始识河南门下诀。到头终得晦翁传之语。可见其千载断案。而世衰道微。或不能致慎于尊卫之地。良可寒心。时当一道睽乖之际。乃作书于绍院疏厅。以为尊贤卫道。自有道理。姑停疏行。以俟公议。公不喜著述。尝曰。吾平生读书。未尝留心于为文。故不得力于文辞。尤不能于诗。先师尝曰。诗。儒者之乐歌。劝令为之。而吾犹不知有益于身心。罕有所作。盖其文辞之可徵者。不越乎经传义理之说。寒暄祭诔之篇。而皆典重温雅。理趣俱到。粹然出于有德者之口。尽所谓布帛菽粟之文也。呜呼。公之资美志笃。得于天赋。不待督责。而脚跟已牢。出入于立损之门。而极力磨砻。决意自进。勉焉孜孜。死而后已。若言其本来田地。则亶由于心学之真切。试以程复心心学图论。蔼然子谅之心。不失本心之正。纯然赤子之心。期造大人之心。人心之危。几乎精察而安。道心之微。几乎一守而著。存心而应物。虚心而处人者。都由于诚之一字。是则一言而蔽公之百行矣。承洙所以用私谥而诔以诚。诚不诬矣。大本既立。无推不去。孝友之行。可质于神明。忠信之著。自孚于日用。慥慥
屈指中间历几贤。始识河南门下诀。到头终得晦翁传之语。可见其千载断案。而世衰道微。或不能致慎于尊卫之地。良可寒心。时当一道睽乖之际。乃作书于绍院疏厅。以为尊贤卫道。自有道理。姑停疏行。以俟公议。公不喜著述。尝曰。吾平生读书。未尝留心于为文。故不得力于文辞。尤不能于诗。先师尝曰。诗。儒者之乐歌。劝令为之。而吾犹不知有益于身心。罕有所作。盖其文辞之可徵者。不越乎经传义理之说。寒暄祭诔之篇。而皆典重温雅。理趣俱到。粹然出于有德者之口。尽所谓布帛菽粟之文也。呜呼。公之资美志笃。得于天赋。不待督责。而脚跟已牢。出入于立损之门。而极力磨砻。决意自进。勉焉孜孜。死而后已。若言其本来田地。则亶由于心学之真切。试以程复心心学图论。蔼然子谅之心。不失本心之正。纯然赤子之心。期造大人之心。人心之危。几乎精察而安。道心之微。几乎一守而著。存心而应物。虚心而处人者。都由于诚之一字。是则一言而蔽公之百行矣。承洙所以用私谥而诔以诚。诚不诬矣。大本既立。无推不去。孝友之行。可质于神明。忠信之著。自孚于日用。慥慥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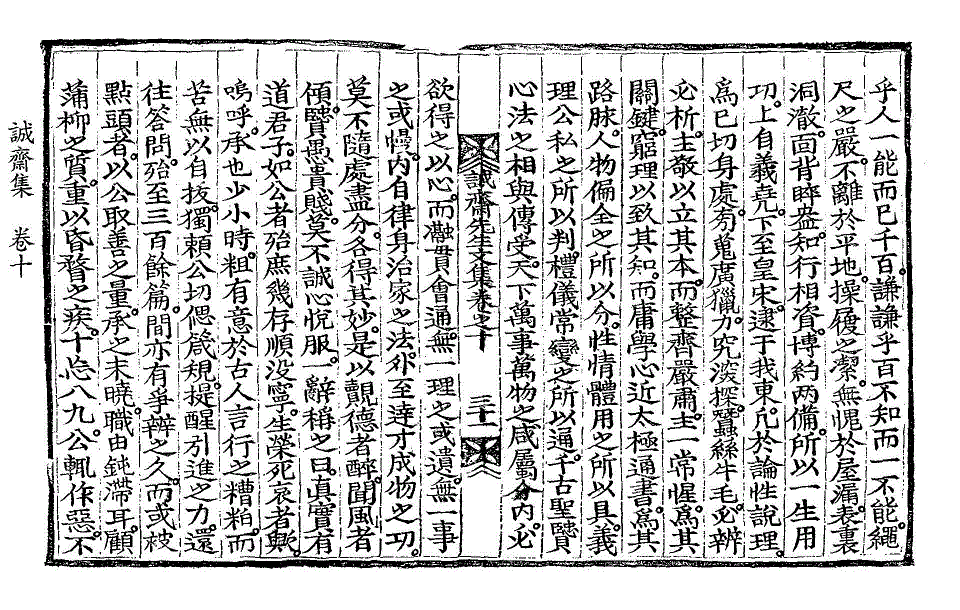 乎人一能而己千百。谦谦乎百不知而一不能。绳尺之严。不离于平地。操履之洁。无愧于屋漏。表里洞澈。面背睟盎。知行相资。博约两备。所以一生用功。上自羲尧。下至皇宋。逮于我东。凡于论性说理。为己切身处。旁蒐广猎。力究深探。蚕丝牛毛。必辨必析。主敬以立其本。而整齐严肃。主一常惺。为其关键。穷理以致其知。而庸学心近太极通书。为其路脉。人物偏全之所以分。性情体用之所以具。义理公私之所以判。礼仪常变之所以通。千古圣贤心法之相与传受。天下万事万物之咸属分内。必欲得之以心。而融贯会通。无一理之或遗。无一事之或慢。内自律身治家之法。外至达才成物之功。莫不随处尽分。各得其妙。是以觌德者醉。闻风者倾。贤愚贵贱。莫不诚心悦服。一辞称之曰。真实有道君子。如公者殆庶几存顺没宁。生荣死哀者欤。呜呼。承也少小时。粗有意于古人言行之糟粕。而苦无以自拔。独赖公切偲箴规。提醒引进之力。还往答问。殆至三百馀篇。间亦有争辨之久。而或被点头者。以公取善之量。承之未晓。职由钝滞耳。顾蒲柳之质。重以昏瞀之疾。十忘八九。公辄作恶。不
乎人一能而己千百。谦谦乎百不知而一不能。绳尺之严。不离于平地。操履之洁。无愧于屋漏。表里洞澈。面背睟盎。知行相资。博约两备。所以一生用功。上自羲尧。下至皇宋。逮于我东。凡于论性说理。为己切身处。旁蒐广猎。力究深探。蚕丝牛毛。必辨必析。主敬以立其本。而整齐严肃。主一常惺。为其关键。穷理以致其知。而庸学心近太极通书。为其路脉。人物偏全之所以分。性情体用之所以具。义理公私之所以判。礼仪常变之所以通。千古圣贤心法之相与传受。天下万事万物之咸属分内。必欲得之以心。而融贯会通。无一理之或遗。无一事之或慢。内自律身治家之法。外至达才成物之功。莫不随处尽分。各得其妙。是以觌德者醉。闻风者倾。贤愚贵贱。莫不诚心悦服。一辞称之曰。真实有道君子。如公者殆庶几存顺没宁。生荣死哀者欤。呜呼。承也少小时。粗有意于古人言行之糟粕。而苦无以自拔。独赖公切偲箴规。提醒引进之力。还往答问。殆至三百馀篇。间亦有争辨之久。而或被点头者。以公取善之量。承之未晓。职由钝滞耳。顾蒲柳之质。重以昏瞀之疾。十忘八九。公辄作恶。不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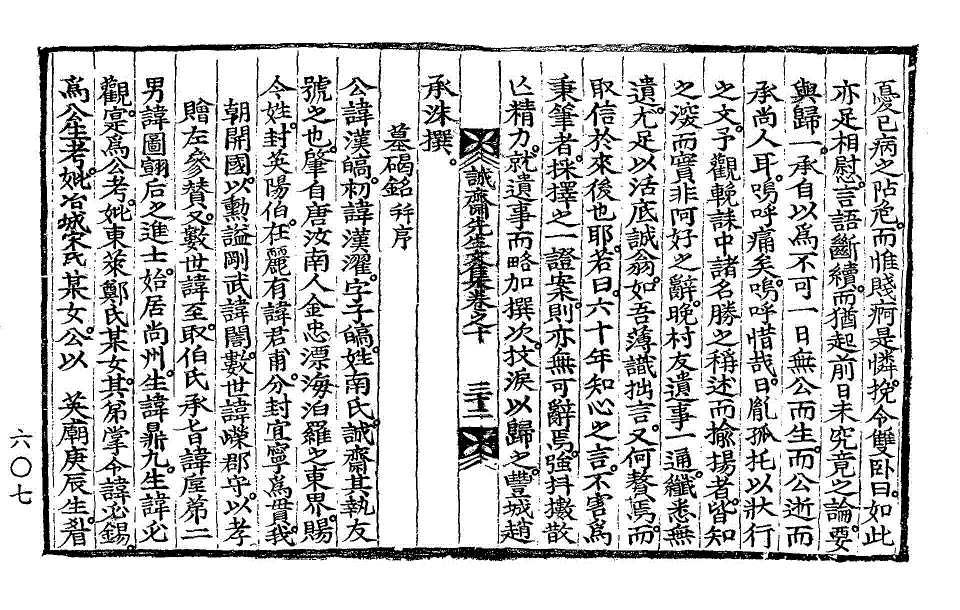 忧己病之阽危。而惟贱痾是怜。挽令双卧曰。如此亦足相慰。言语断续。而犹起前日未究竟之论。要与归一。承自以为不可一日无公而生。而公逝而承尚人耳。呜呼痛矣。呜呼惜哉。日胤孤托以状行之文。予观挽诔中诸名胜之称述而揄扬者。皆知之深而实非阿好之辞。晚村友遗事一通。纤悉无遗。尤足以活底诚翁。如吾薄识拙言。又何赘焉。而取信于来后也耶。若曰。六十年知心之言。不害为秉笔者。采择之一證案。则亦无可辞焉。强抖擞散亡精力。就遗事而略加撰次。抆泪以归之。丰城赵承洙撰。
忧己病之阽危。而惟贱痾是怜。挽令双卧曰。如此亦足相慰。言语断续。而犹起前日未究竟之论。要与归一。承自以为不可一日无公而生。而公逝而承尚人耳。呜呼痛矣。呜呼惜哉。日胤孤托以状行之文。予观挽诔中诸名胜之称述而揄扬者。皆知之深而实非阿好之辞。晚村友遗事一通。纤悉无遗。尤足以活底诚翁。如吾薄识拙言。又何赘焉。而取信于来后也耶。若曰。六十年知心之言。不害为秉笔者。采择之一證案。则亦无可辞焉。强抖擞散亡精力。就遗事而略加撰次。抆泪以归之。丰城赵承洙撰。墓碣铭(并序)[柳致明]
公讳汉皓。初讳汉濯。字子皓。姓南氏。诚斋其执友号之也。肇自唐汝南人金忠漂海泊罗之东界。赐今姓。封英阳伯。在丽有讳君甫。分封宜宁为贯。我 朝开国。以勋谥刚武讳訚。数世讳嵘郡守。以孝 赠左参赞。又数世讳至。取伯氏承旨讳垕第二男讳图翧后之进士。始居尚州。生讳鼎九。生讳必观。寔为公考。妣东莱郑氏某女。其弟掌令讳必锡。为公生考。妣冶城宋氏某女。公以 英庙庚辰生。眉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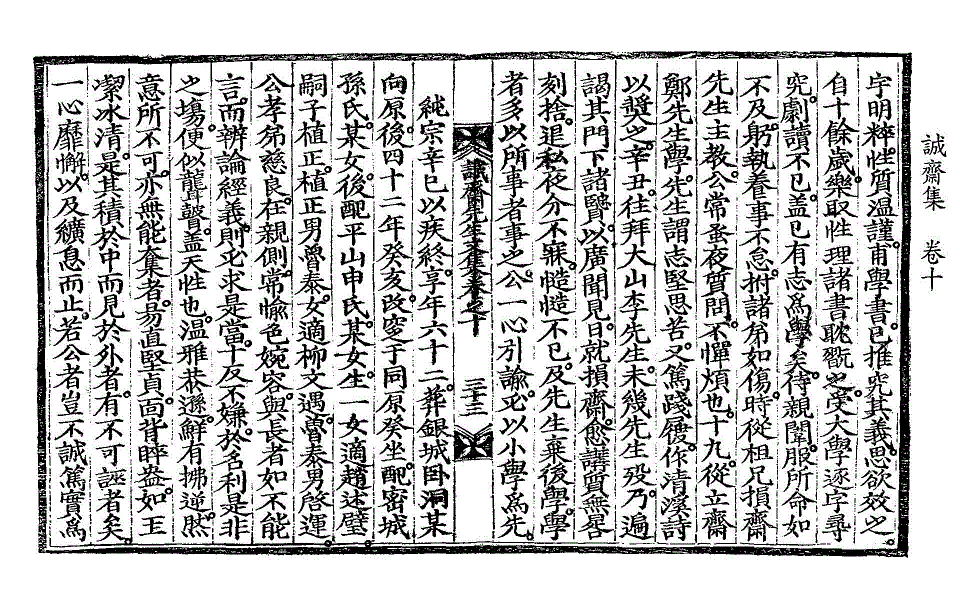 宇明粹。性质温谨。甫学书。已推究其义。思欲效之。自十馀岁。乐取性理诸书耽玩之。受大学逐字寻究。剧读不已。盖已有志为学矣。侍亲闱。服所命如不及。躬执养事不怠。拊诸弟如伤。时从祖兄损斋先生主教。公常蚤夜质问。不惮烦也。十九。从立斋郑先生学。先生谓志坚思苦。又笃践履。作清溪诗以奖之。辛丑。往拜大山李先生。未几先生殁。乃遍谒其门下诸贤。以广闻见。日就损斋。愈讲质无晷刻舍。退私夜分不寐。慥慥不已。及先生弃后学。学者多以所事者事之。公一心引谕。必以小学为先。 纯宗辛巳以疾终。享年六十二。葬银城卧洞某向原。后四十二年癸亥。改窆于同原癸坐。配密城孙氏。某女。后配平山申氏。某女。生一女适赵述璧。嗣子植正。植正男鲁泰。女适柳文遇。鲁泰男启运。公孝弟慈良。在亲侧。常愉色婉容。与长者如不能言。而辨论经义。则必求是当。十反不嫌。于名利是非之场。便似聋𥌒。盖天性也。温雅恭逊。鲜有拂逆。然意所不可。亦无能夺者。易直坚贞。面背睟盎。如玉洁冰清。是其积于中而见于外者。有不可诬者矣。一心靡懈。以及纩息而止。苦公者岂不诚笃实为
宇明粹。性质温谨。甫学书。已推究其义。思欲效之。自十馀岁。乐取性理诸书耽玩之。受大学逐字寻究。剧读不已。盖已有志为学矣。侍亲闱。服所命如不及。躬执养事不怠。拊诸弟如伤。时从祖兄损斋先生主教。公常蚤夜质问。不惮烦也。十九。从立斋郑先生学。先生谓志坚思苦。又笃践履。作清溪诗以奖之。辛丑。往拜大山李先生。未几先生殁。乃遍谒其门下诸贤。以广闻见。日就损斋。愈讲质无晷刻舍。退私夜分不寐。慥慥不已。及先生弃后学。学者多以所事者事之。公一心引谕。必以小学为先。 纯宗辛巳以疾终。享年六十二。葬银城卧洞某向原。后四十二年癸亥。改窆于同原癸坐。配密城孙氏。某女。后配平山申氏。某女。生一女适赵述璧。嗣子植正。植正男鲁泰。女适柳文遇。鲁泰男启运。公孝弟慈良。在亲侧。常愉色婉容。与长者如不能言。而辨论经义。则必求是当。十反不嫌。于名利是非之场。便似聋𥌒。盖天性也。温雅恭逊。鲜有拂逆。然意所不可。亦无能夺者。易直坚贞。面背睟盎。如玉洁冰清。是其积于中而见于外者。有不可诬者矣。一心靡懈。以及纩息而止。苦公者岂不诚笃实为诚斋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6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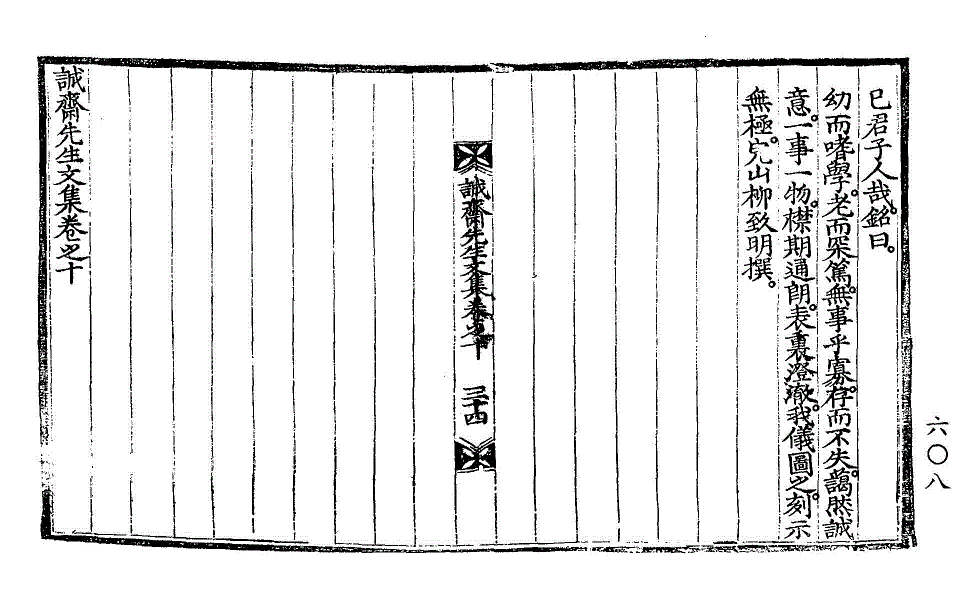 己君子人哉。铭曰。
己君子人哉。铭曰。幼而嗜学。老而深笃。无事乎寡。存而不失。蔼然诚意。一事一物。襟期通朗。表里澄澈。我仪图之。刻示无极。完山柳致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