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x 页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书
书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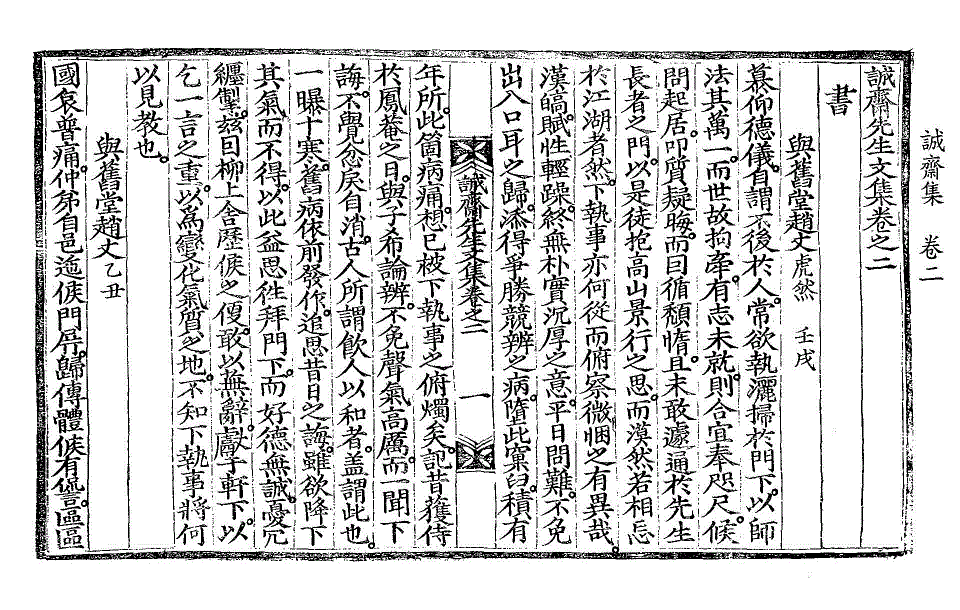 与旧堂赵丈(虎然○壬戌)
与旧堂赵丈(虎然○壬戌)慕仰德仪。自谓不后于人。常欲执洒扫于门下。以师法其万一。而世故拘牵。有志未就。则合宜奉咫尺。候问起居。叩质疑晦。而因循颓惰。且未敢遽通于先生长者之门。以是徒抱高山景行之思。而漠然若相忘于江湖者然。下执事亦何从而俯察微悃之有异哉。汉皓。赋性轻躁。终无朴实沉厚之意。平日问难。不免出入口耳之归。添得争胜竞辨之病。堕此窠臼。积有年所。此个病痛。想已被下执事之俯烛矣。记昔获侍于凤庵之日。与子希论辨。不免声气高厉。而一闻下诲。不觉忿戾自消。古人所谓饮人以和者。盖谓此也。一曝十寒。旧病依前发作。追思昔日之诲。虽欲降下其气而不得。以此益思往拜门下。而好德无诚。忧冗缠掣。玆因柳上舍历候之便。敢以芜辞。献于轩下。以乞一言之重。以为变化气质之地。不知下执事将何以见教也。
与旧堂赵丈(乙丑)
国哀普痛。仲弟自邑迤候门屏。归传体候有愆。区区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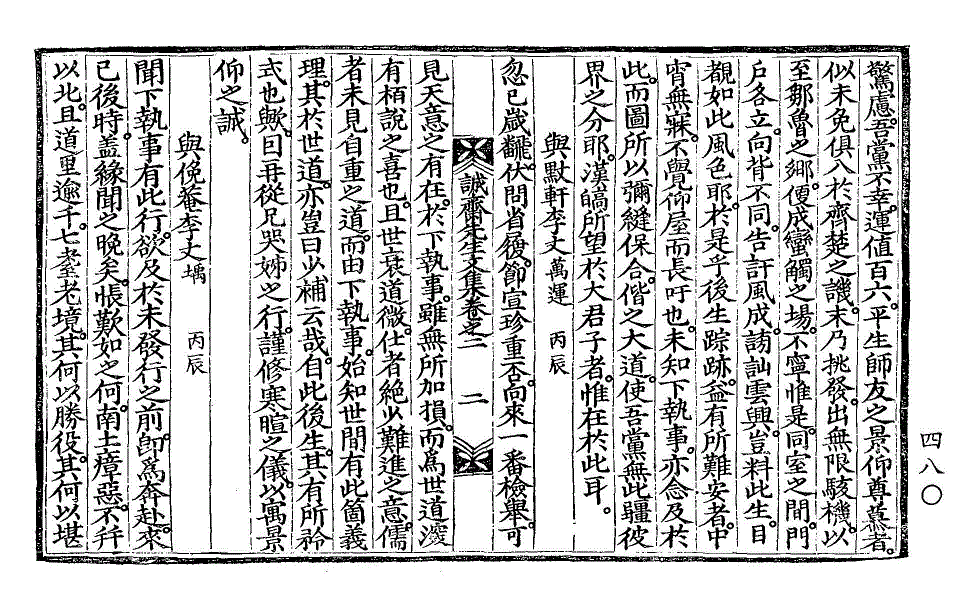 惊虑。吾党不幸。运值百六。平生师友之景仰尊慕者。似未免俱入于齐楚之讥。末乃挑发。出无限骇机。以至邹鲁之乡。便成蛮触之场。不宁惟是。同室之间。门户各立。向背不同。告讦风成。谤讪云兴。岂料此生。目睹如此风色耶。于是乎后生踪迹。益有所难安者。中宵无寐。不觉仰屋而长吁也。未知下执事。亦念及于此。而图所以弥缝保合。偕之大道。使吾党无此疆彼界之分耶。汉皓所望于大君子者。惟在于此耳。
惊虑。吾党不幸。运值百六。平生师友之景仰尊慕者。似未免俱入于齐楚之讥。末乃挑发。出无限骇机。以至邹鲁之乡。便成蛮触之场。不宁惟是。同室之间。门户各立。向背不同。告讦风成。谤讪云兴。岂料此生。目睹如此风色耶。于是乎后生踪迹。益有所难安者。中宵无寐。不觉仰屋而长吁也。未知下执事。亦念及于此。而图所以弥缝保合。偕之大道。使吾党无此疆彼界之分耶。汉皓所望于大君子者。惟在于此耳。与默轩李丈(万运○丙辰)
忽已岁翻。伏问省履。节宣珍重否。向来一番检举。可见天意之有在。于下执事。虽无所加损。而为世道深有柏说之喜也。且世衰道微。仕者绝少难进之意。儒者未见自重之道。而由下执事。始知世间有此个义理。其于世道。亦岂曰少补云哉。自此后生。其有所矜式也欤。因再从兄哭姊之行。谨修寒暄之仪。以寓景仰之诚。
与俛庵李丈(㙖○丙辰)
闻下执事有此行。欲及于未发行之前。即为奔赴。来已后时。盖缘闻之晚矣。怅叹如之何。南土瘴恶。不并以北。且道里逾千。七耋老境。其何以胜役。其何以堪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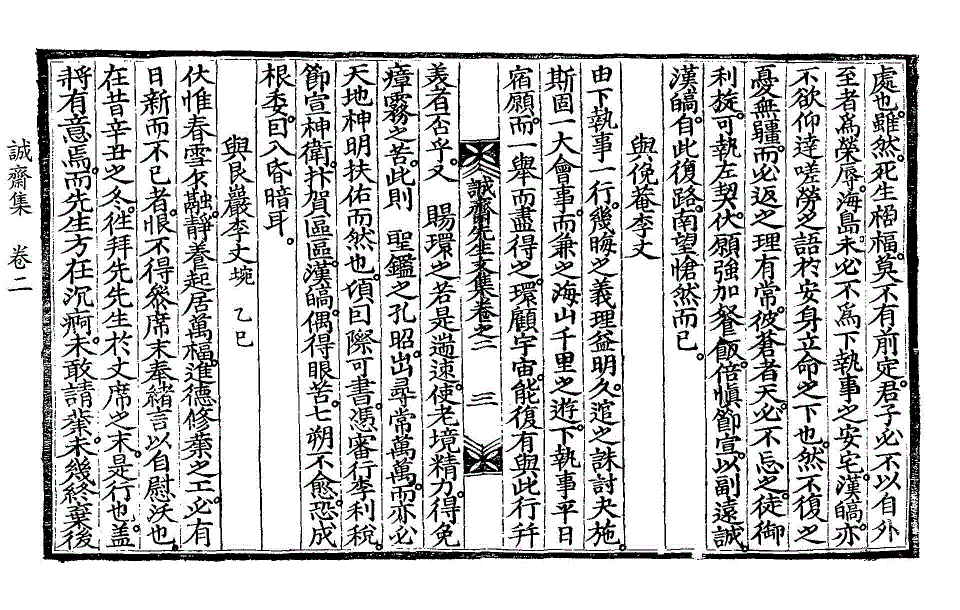 处也。虽然。死生祸福。莫不有前定。君子必不以自外至者为荣辱。海岛。未必不为下执事之安宅。汉皓。亦不欲仰达嗟劳之语于安身立命之下也。然不复之忧无疆。而必返之理有常。彼苍者天。必不忘之。徒御利旋。可执左契。伏愿强加餐饭。倍慎节宣。以副远诚。汉皓。自此复路。南望怆然而已。
处也。虽然。死生祸福。莫不有前定。君子必不以自外至者为荣辱。海岛。未必不为下执事之安宅。汉皓。亦不欲仰达嗟劳之语于安身立命之下也。然不复之忧无疆。而必返之理有常。彼苍者天。必不忘之。徒御利旋。可执左契。伏愿强加餐饭。倍慎节宣。以副远诚。汉皓。自此复路。南望怆然而已。与俛庵李丈
由下执事一行。几晦之义理益明。久逭之诛讨夬施。斯固一大会事。而兼之海山千里之游。下执事平日宿愿。而一举而尽得之。环顾宇宙。能复有与此行并美者否乎。又 赐环之若是遄速。使老境精力。得免瘴雾之苦。此则 圣鉴之孔昭。出寻常万万。而亦必天地神明扶佑而然也。顷因际可书。凭审行李利税。节宣神卫。抃贺区区。汉皓。偶得眼苦。七朔不愈。恐成根委。因入昏暗耳。
与艮岩李丈(埦○乙巳)
伏惟春雪乍融。静养起居万福。进德修业之工。必有日新而不已者。恨不得参席末奉绪言以自慰沃也。在昔辛丑之冬。往拜先先生于丈席之末。是行也。盖将有意焉。而先生方在沉痾。未敢请业。未几终弃后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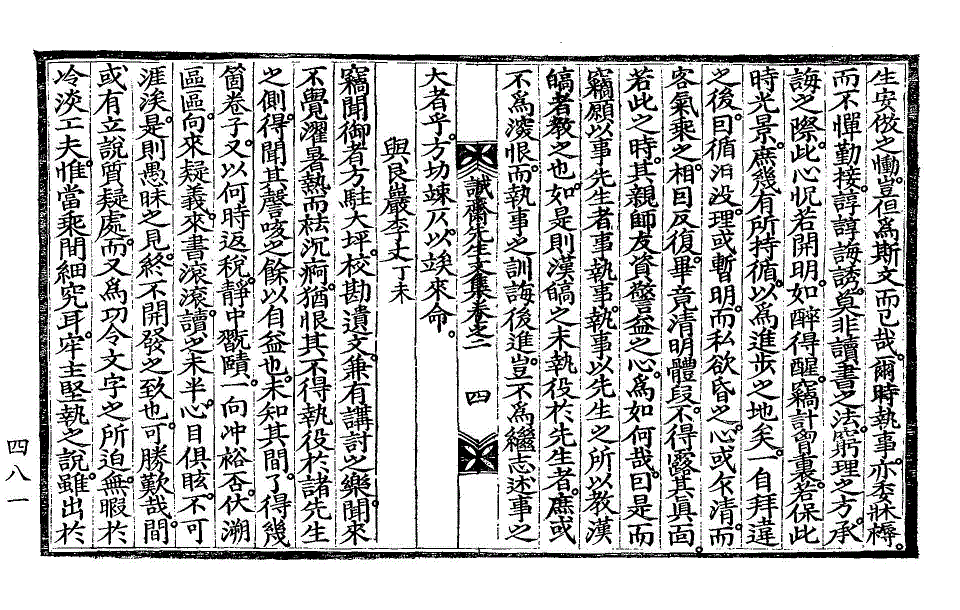 生安仿之恸。岂但为斯文而已哉。尔时执事。亦委床褥。而不惮勤接。谆谆诲诱。莫非读书之法。穷理之方。承诲之际。此心恍若开明。如醉得醒。窃计胸里。若保此时光景。庶几有所持循。以为进步之地矣。一自拜违之后。因循汩没。理或暂明。而私欲昏之。心或乍清。而客气乘之。相因反复。毕竟清明体段。不得露其真面。若此之时。其亲师友资警益之心。为如何哉。因是而窃愿以事先生者事执事。执事以先生之所以教汉皓者教之也。如是则汉皓之未执役于先生者。庶或不为深恨。而执事之训诲后进。岂不为继志述事之大者乎。方切竦仄。以俟来命。
生安仿之恸。岂但为斯文而已哉。尔时执事。亦委床褥。而不惮勤接。谆谆诲诱。莫非读书之法。穷理之方。承诲之际。此心恍若开明。如醉得醒。窃计胸里。若保此时光景。庶几有所持循。以为进步之地矣。一自拜违之后。因循汩没。理或暂明。而私欲昏之。心或乍清。而客气乘之。相因反复。毕竟清明体段。不得露其真面。若此之时。其亲师友资警益之心。为如何哉。因是而窃愿以事先生者事执事。执事以先生之所以教汉皓者教之也。如是则汉皓之未执役于先生者。庶或不为深恨。而执事之训诲后进。岂不为继志述事之大者乎。方切竦仄。以俟来命。与艮岩李丈(丁未)
窃闻御者方驻大坪。校勘遗文。兼有讲讨之乐。闻来不觉濯暑热而祛沉痾。犹恨其不得执役于诸先生之侧。得闻其謦咳之馀以自益也。未知其间。了得几个卷子。又以何时返税。静中玩赜。一向冲裕否。伏溯区区。向来疑义。来书滚滚。读之未半。心目俱眩。不可涯涘。是则愚昧之见。终不开发之致也。可胜叹哉。间或有立说质疑处。而又为功令文字之所迫。无暇于冷淡工夫。惟当乘间细究耳。牢主坚执之说。虽出于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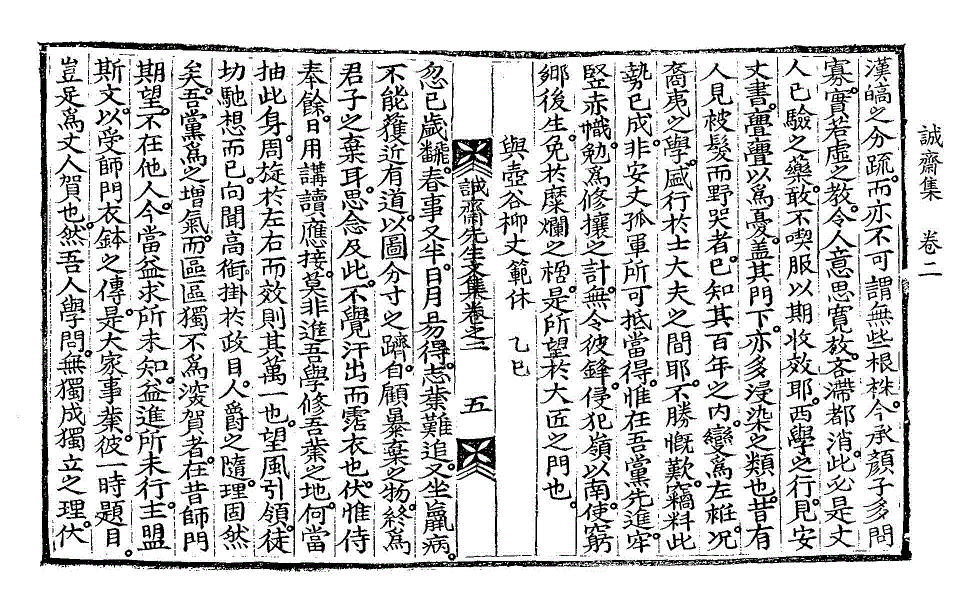 汉皓之分疏。而亦不可谓无些根株。今承颜子多问寡。实若虚之教。令人意思宽放。吝滞都消。此必是丈人已验之药。敢不吃服以期收效耶。西学之行。见安丈书。亹亹以为忧。盖其门下。亦多浸染之类也。昔有人见被发而野哭者。已知其百年之内。变为左衽。况裔夷之学。盛行于士大夫之间耶。不胜慨叹。窃料此势已成。非安丈孤军所可抵当得。惟在吾党先进。牢竖赤帜。勉为修攘之计。无令彼锋。侵犯岭以南。使穷乡后生。免于糜烂之祸。是所望于大匠之门也。
汉皓之分疏。而亦不可谓无些根株。今承颜子多问寡。实若虚之教。令人意思宽放。吝滞都消。此必是丈人已验之药。敢不吃服以期收效耶。西学之行。见安丈书。亹亹以为忧。盖其门下。亦多浸染之类也。昔有人见被发而野哭者。已知其百年之内。变为左衽。况裔夷之学。盛行于士大夫之间耶。不胜慨叹。窃料此势已成。非安丈孤军所可抵当得。惟在吾党先进。牢竖赤帜。勉为修攘之计。无令彼锋。侵犯岭以南。使穷乡后生。免于糜烂之祸。是所望于大匠之门也。与壶谷柳丈(范休○乙巳)
忽已岁翻。春事又半。日月易得。志业难追。又坐羸病。不能获近有道。以图分寸之跻。自顾㬥弃之物。终为君子之弃耳。思念及此。不觉汗出而沾衣也。伏惟侍奉馀。日用讲读应接。莫非进吾学修吾业之地。何当抽此身。周旋于左右而效则其万一也。望风引领。徒切驰想而已。向闻高衔挂于政目。人爵之随。理固然矣。吾党为之增气。而区区独不为深贺者。在昔师门期望。不在他人。今当益求所未知。益进所未行。主盟斯文。以受师门衣钵之传。是大家事业。彼一时题目。岂足为丈人贺也。然吾人学问。无独成独立之理。伏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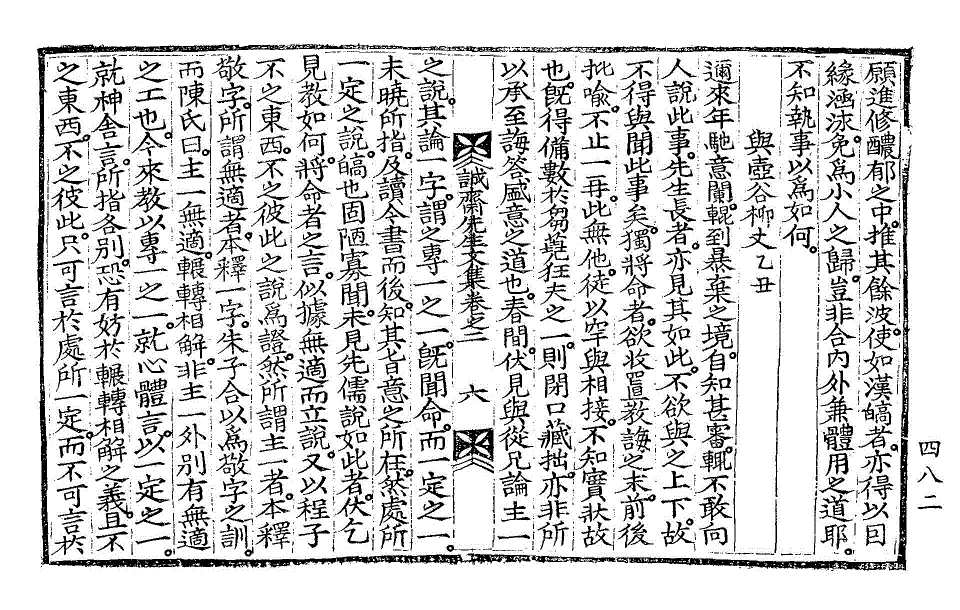 愿进修醲郁之中。推其馀波。使如汉皓者。亦得以因缘涵泳。免为小人之归。岂非合内外兼体用之道耶。不知执事以为如何。
愿进修醲郁之中。推其馀波。使如汉皓者。亦得以因缘涵泳。免为小人之归。岂非合内外兼体用之道耶。不知执事以为如何。与壶谷柳丈(乙丑)
迩来年驰意阑。辊到暴弃之境。自知甚审。辄不敢向人说此事。先生长者。亦见其如此。不欲与之上下。故不得与闻此事矣。独将命者。欲收置教诲之末。前后批喻。不止一再。此无他。徒以罕与相接。不知实状故也。既得备数于刍荛狂夫之一。则闭口藏拙。亦非所以承至诲答盛意之道也。春间。伏见与从兄论主一之说。其论一字。谓之专一之一。既闻命。而一定之一。未晓所指。及读今书而后。知其旨意之所在。然处所一定之说。皓也固陋寡闻。未见先儒说如此者。伏乞见教如何。将命者之言。似据无适而立说。又以程子不之东西。不之彼此之说为證。然所谓主一者。本释敬字。所谓无适者。本释一字。朱子合以为敬字之训。而陈氏曰。主一无适。辗转相解。非主一外别有无适之工也。今来教以专一之一。就心体言。以一定之一。就神舍言。所指各别。恐有妨于辗转相解之义。且不之东西。不之彼此。只可言于处所一定。而不可言于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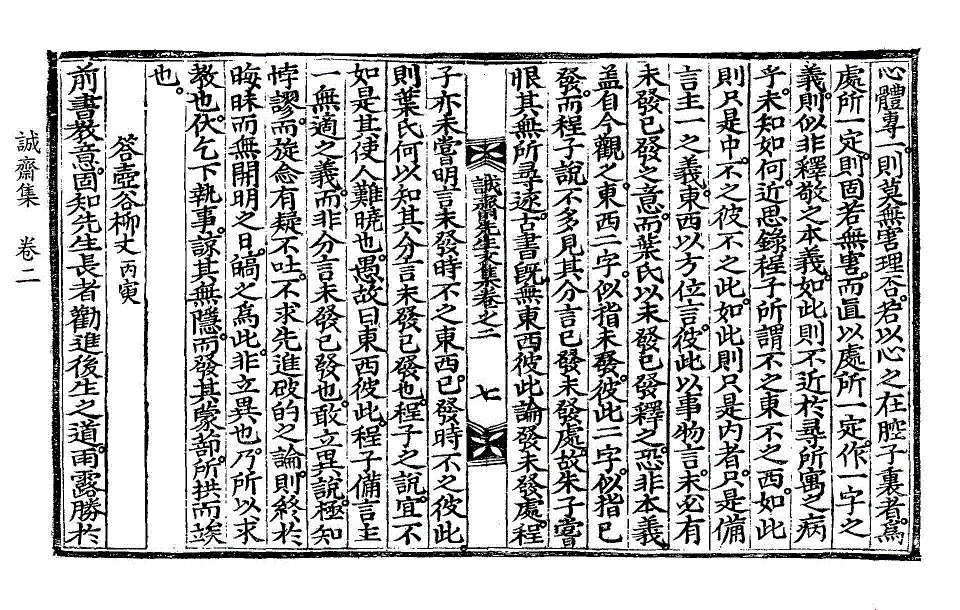 心体专一。则莫无害理否。若以心之在腔子里者。为处所一定。则固若无害。而直以处所一定。作一字之义。则似非释敬之本义。如此则不近于寻所寓之病乎。未知如何。近思录程子所谓不之东不之西。如此则只是中。不之彼不之此。如此则只是内者。只是备言主一之义。东西以方位言。彼此以事物言。未必有未发已发之意。而叶氏以未发已发释之。恐非本义。盖自今观之。东西二字。似指未发。彼此二字。似指已发。而程子说不多见其分言已发未发处。故朱子尝恨其无所寻逐。古书既无东西彼此论发未发处。程子亦未尝明言未发时不之东西。已发时不之彼此。则叶氏何以知其分言未发已发也。程子之说。宜不如是其使人难晓也。愚故曰东西彼此。程子备言主一无适之义。而非分言未发已发也。敢立异说。极知悖谬。而旋念有疑不吐。不求先进破的之论。则终于晦昧而无开明之日。皓之为此。非立异也。乃所以求教也。伏乞下执事。谅其无隐。而发其蒙蔀。所拱而俟也。
心体专一。则莫无害理否。若以心之在腔子里者。为处所一定。则固若无害。而直以处所一定。作一字之义。则似非释敬之本义。如此则不近于寻所寓之病乎。未知如何。近思录程子所谓不之东不之西。如此则只是中。不之彼不之此。如此则只是内者。只是备言主一之义。东西以方位言。彼此以事物言。未必有未发已发之意。而叶氏以未发已发释之。恐非本义。盖自今观之。东西二字。似指未发。彼此二字。似指已发。而程子说不多见其分言已发未发处。故朱子尝恨其无所寻逐。古书既无东西彼此论发未发处。程子亦未尝明言未发时不之东西。已发时不之彼此。则叶氏何以知其分言未发已发也。程子之说。宜不如是其使人难晓也。愚故曰东西彼此。程子备言主一无适之义。而非分言未发已发也。敢立异说。极知悖谬。而旋念有疑不吐。不求先进破的之论。则终于晦昧而无开明之日。皓之为此。非立异也。乃所以求教也。伏乞下执事。谅其无隐。而发其蒙蔀。所拱而俟也。答壶谷柳丈(丙寅)
前书教意。固知先生长者劝进后生之道。雨露胜于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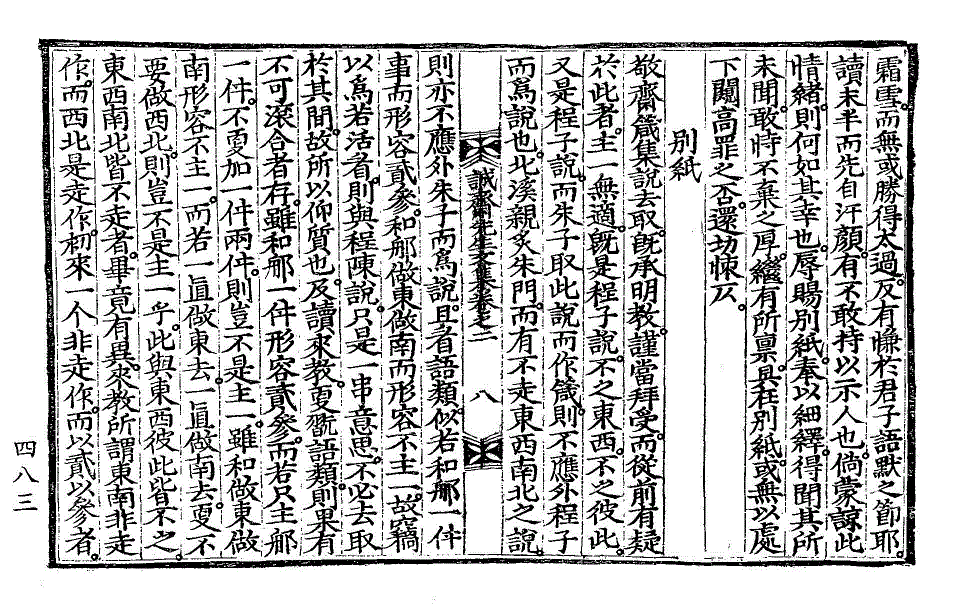 霜雪。而无或胜得太过。反有慊于君子语默之节耶。读未半而先自汗颜。有不敢持以示人也。倘蒙谅此情绪。则何如其幸也。辱赐别纸。奉以细绎。得闻其所未闻。敢恃不弃之厚。继有所禀。具在别纸。或无以处下窥高罪之否。还切悚仄。
霜雪。而无或胜得太过。反有慊于君子语默之节耶。读未半而先自汗颜。有不敢持以示人也。倘蒙谅此情绪。则何如其幸也。辱赐别纸。奉以细绎。得闻其所未闻。敢恃不弃之厚。继有所禀。具在别纸。或无以处下窥高罪之否。还切悚仄。别纸
敬斋箴集说去取。既承明教。谨当拜受。而从前有疑于此者。主一无适。既是程子说。不之东西。不之彼此。又是程子说。而朱子取此说而作箴。则不应外程子而为说也。北溪亲炙朱门。而有不走东西南北之说。则亦不应外朱子而为说。且看语类。似若和那一件事而形容贰参。和那做东做南而形容不主一。故窃以为若活看。则与程陈说。只是一串意思。不必去取于其间。故所以仰质也。及读来教。更玩语类。则果有不可滚合者存。虽和那一件形容贰参。而若只主那一件。不更加一件两件。则岂不是主一。虽和做东做南形容不主一。而若一直做东去。一直做南去。更不要做西北。则岂不是主一乎。此与东西彼此皆不之。东西南北皆不走者。毕竟有异。来教所谓东南非走作。而西北是走作。初来一个非走作。而以贰以参者。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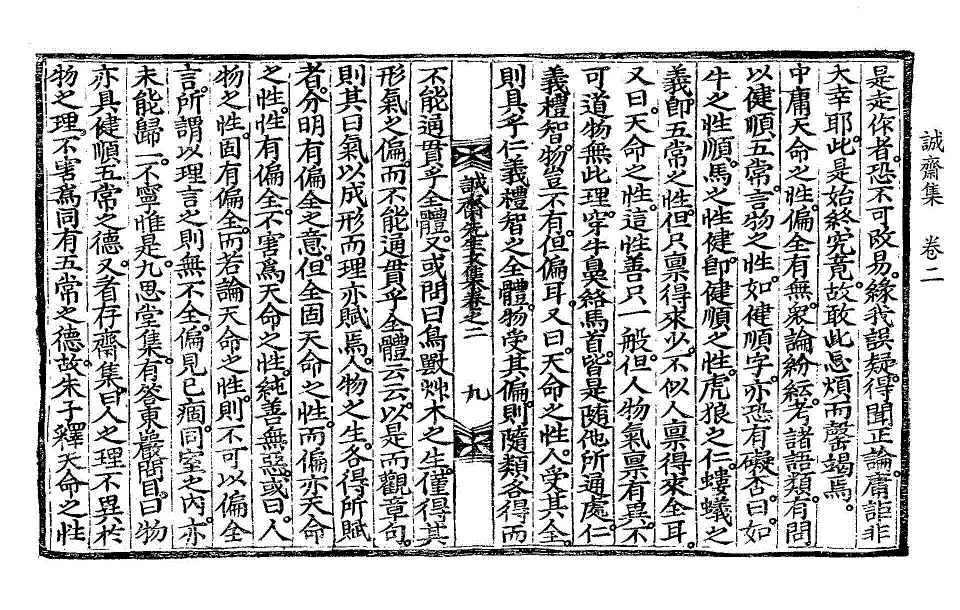 是走作者。恐不可改易。缘我误疑。得闻正论。庸讵非大幸耶。此是始终究竟。故敢此忘烦而罄竭焉。
是走作者。恐不可改易。缘我误疑。得闻正论。庸讵非大幸耶。此是始终究竟。故敢此忘烦而罄竭焉。中庸天命之性。偏全有无。众论纷纭。考诸语类。有问以健顺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顺字。亦恐有碍否。曰。如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蝼蚁之义。即五常之性。但只禀得来少。不似人禀得来全耳。又曰。天命之性。这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穿牛鼻络马首。皆是随他所通处。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又曰。天命之性。人受其全。则具乎仁义礼智之全体。物受其偏。则随类各得而不能通贯乎全体。又或问曰鸟兽草木之生。仅得其形气之偏。而不能通贯乎全体云云。以是而观章句。则其曰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人物之生。各得所赋者。分明有偏全之意。但全固天命之性。而偏亦天命之性。性有偏全。不害为天命之性。纯善无恶。或曰。人物之性。固有偏全。而若论天命之性。则不可以偏全言。所谓以理言之则无不全。偏见已痼。同室之内。亦未能归一。不宁惟是。九思堂集。有答东岩问目。曰物亦具健顺五常之德。又看存斋集。曰人之理不异于物之理。不害为同有五常之德。故朱子释天命之性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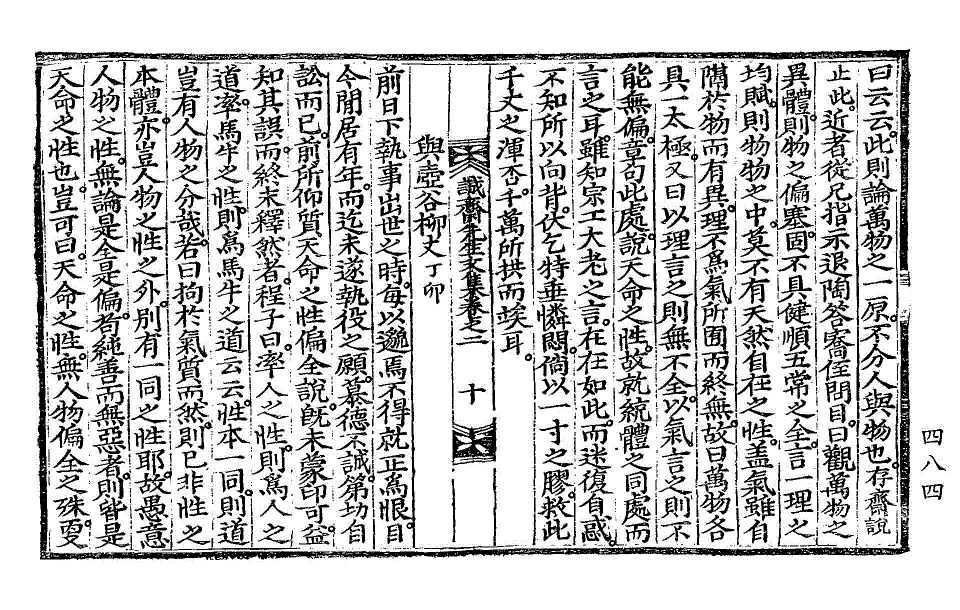 曰云云。此则论万物之一原。不分人与物也。(存斋说止此。)近者从兄指示退陶答㝯侄问目。曰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固不具健顺五常之全。言一理之均赋。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然自在之性。盖气虽自隔于物而有异。理不为气所囿而终无。故曰万物各具一太极。又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章句此处。说天命之性。故就统体之同处而言之耳。虽知宗工大老之言。在在如此。而迷复自惑。不知所以向背。伏乞特垂怜闷。倘以一寸之胶。救此千丈之浑否。千万所拱而俟耳。
曰云云。此则论万物之一原。不分人与物也。(存斋说止此。)近者从兄指示退陶答㝯侄问目。曰观万物之异体。则物之偏塞。固不具健顺五常之全。言一理之均赋。则物物之中。莫不有天然自在之性。盖气虽自隔于物而有异。理不为气所囿而终无。故曰万物各具一太极。又曰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章句此处。说天命之性。故就统体之同处而言之耳。虽知宗工大老之言。在在如此。而迷复自惑。不知所以向背。伏乞特垂怜闷。倘以一寸之胶。救此千丈之浑否。千万所拱而俟耳。与壶谷柳丈(丁卯)
前日下执事出世之时。每以邈焉不得就正为恨。目今閒居有年。而迄未遂执役之愿。慕德不诚。第切自讼而已。前所仰质天命之性偏全说。既未蒙印可。益知其误。而终未释然者。程子曰。率人之性。则为人之道。率马牛之性。则为马牛之道云云。性本一同。则道岂有人物之分哉。若曰拘于气质而然。则已非性之本体。亦岂人物之性之外。别有一同之性耶。故愚意人物之性。无论是全是偏。苟纯善而无恶者。则皆是天命之性也。岂可曰。天命之性。无人物偏全之殊。更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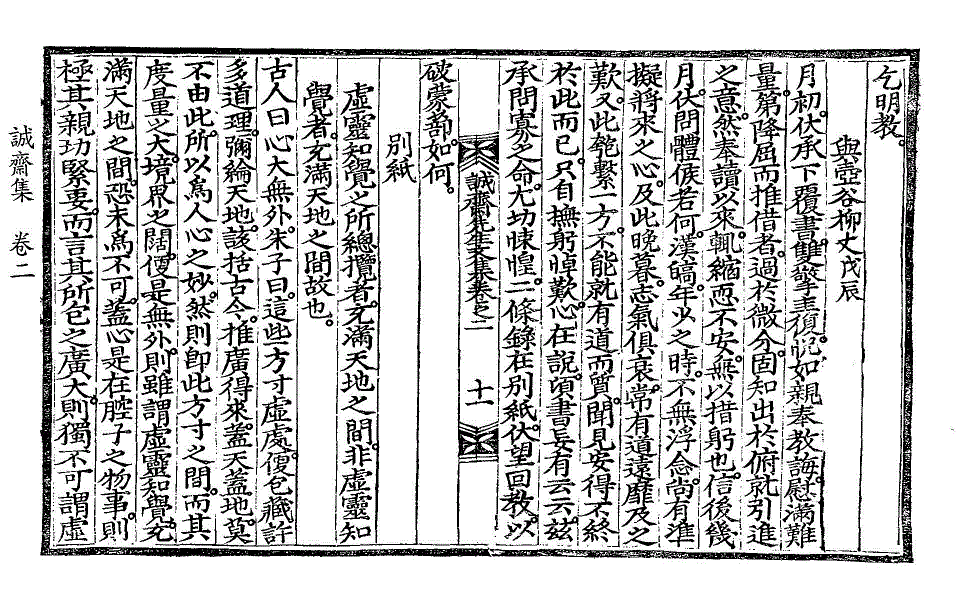 乞明教。
乞明教。与壶谷柳丈(戊辰)
月初。伏承下覆书。双擎圭复。恍如亲奉教诲。慰满难量。第降屈而推借者。过于微分。固知出于俯就引进之意。然奉读以来。辄缩恧不安。无以措躬也。信后几月。伏问体候若何。汉皓。年少之时。不无浮念。尚有准拟将来之心。及此晚暮。志气俱衰。常有道远靡及之叹。又此匏系一方。不能就有道而质。闻见安得不终于此而已。只自抚躬悼叹。心在说。顷书妄有云云。玆承问寡之命。尤切悚惶。二条录在别纸。伏望回教。以破蒙蔀。如何。
别纸
虚灵知觉之所总揽者。充满天地之间。非虚灵知觉者。充满天地之间故也。
古人曰心大无外。朱子曰。这些方寸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弥纶天地。该括古今。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所以为人心之妙。然则即此方寸之间。而其度量之大。境界之阔。便是无外。则虽谓虚灵知觉。充满天地之间。恐未为不可。盖心是在腔子之物事。则极其亲切紧要。而言其所包之广大。则独不可谓虚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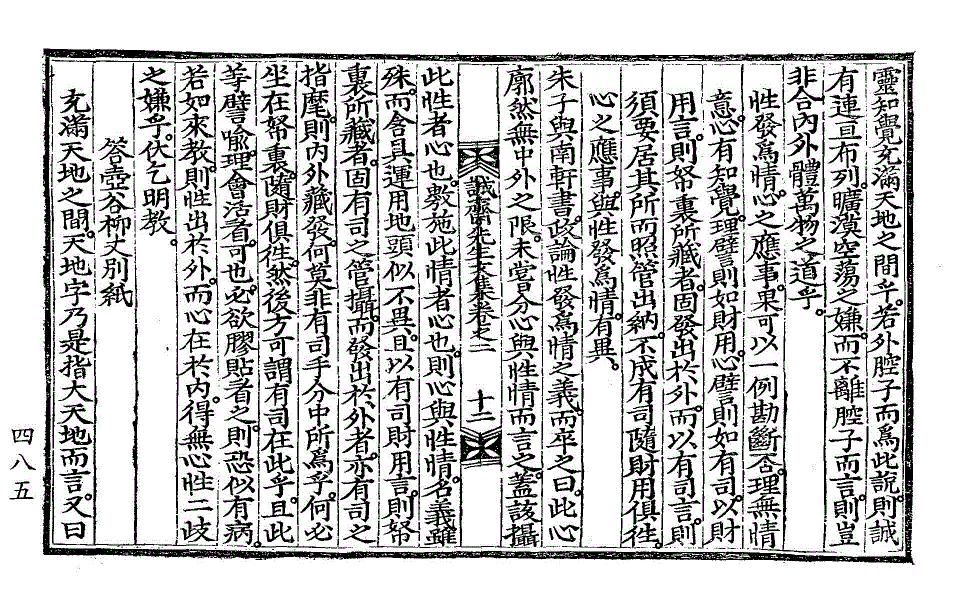 灵知觉充满天地之间乎。若外腔子而为此说。则诚有连亘布列。旷漠空荡之嫌。而不离腔子而言。则岂非合内外体万物之道乎。
灵知觉充满天地之间乎。若外腔子而为此说。则诚有连亘布列。旷漠空荡之嫌。而不离腔子而言。则岂非合内外体万物之道乎。性发为情。心之应事。果可以一例勘断否。理无情意。心有知觉。理譬则如财用。心譬则如有司。以财用言。则帑里所藏者。固发出于外。而以有司言。则须要居其所而照管出纳。不成有司随财用俱往。心之应事。与性发为情。有异。
朱子与南轩书。政论性发为情之义。而卒之曰。此心廓然无中外之限。未尝分心与性情而言之。盖该摄此性者心也。敷施此情者心也。则心与性情。名义虽殊。而含具运用地头似不异。且以有司财用言。则帑里所藏者。固有司之管摄。而发出于外者。亦有司之指麾。则内外藏发。何莫非有司手分中所为乎。何必坐在帑里。随财俱往。然后方可谓有司在此乎。且此等譬喻。理会活看。可也。必欲胶贴看之。则恐似有病。若如来教。则性出于外。而心在于内。得无心性二歧之嫌乎。伏乞明教。
答壶谷柳丈别纸
充满天地之间。天地字乃是指大天地而言。又曰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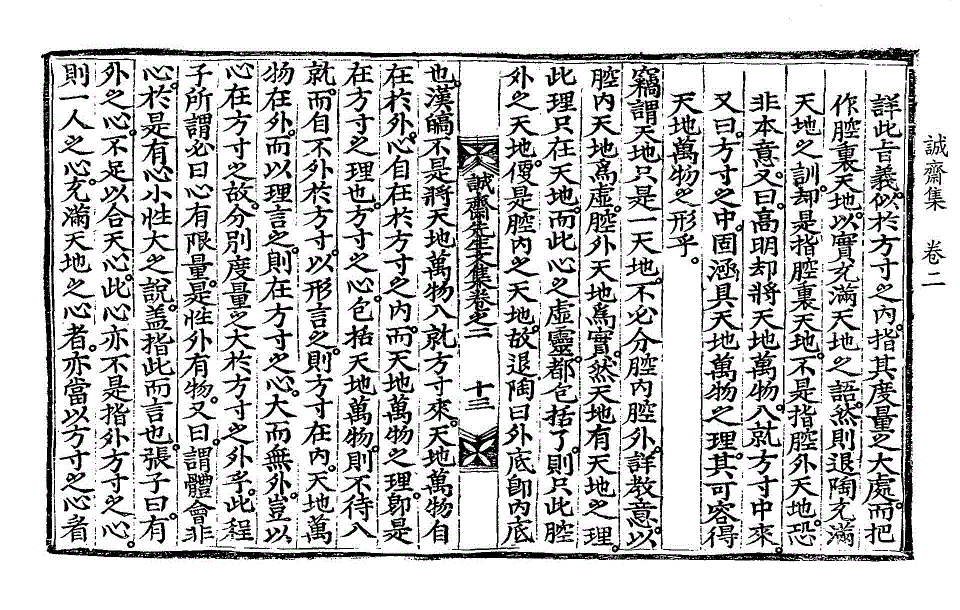 详此旨义。似于方寸之内。指其度量之大处。而把作腔里天地。以实充满天地之语。然则退陶充满天地之训。却是指腔里天地。不是指腔外天地。恐非本意。又曰。高明却将天地万物。入就方寸中来。又曰。方寸之中。固涵具天地万物之理。其可容得天地万物之形乎。
详此旨义。似于方寸之内。指其度量之大处。而把作腔里天地。以实充满天地之语。然则退陶充满天地之训。却是指腔里天地。不是指腔外天地。恐非本意。又曰。高明却将天地万物。入就方寸中来。又曰。方寸之中。固涵具天地万物之理。其可容得天地万物之形乎。窃谓天地只是一天地。不必分腔内腔外。详教意。以腔内天地为虚。腔外天地为实。然天地有天地之理。此理只在天地。而此心之虚灵。都包括了。则只此腔外之天地。便是腔内之天地。故退陶曰外底即内底也。汉皓不是将天地万物入就方寸来。天地万物自在于外。心自在于方寸之内。而天地万物之理。即是在方寸之理也。方寸之心。包括天地万物。则不待入就。而自不外于方寸。以形言之。则方寸在内。天地万物在外。而以理言之。则在方寸之心。大而无外。岂以心在方寸之故。分别度量之大于方寸之外乎。此程子所谓必曰心有限量。是性外有物。又曰。谓体会非心。于是有心小性大之说。盖指此而言也。张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此心亦不是指外方寸之心。则一人之心。充满天地之心者。亦当以方寸之心看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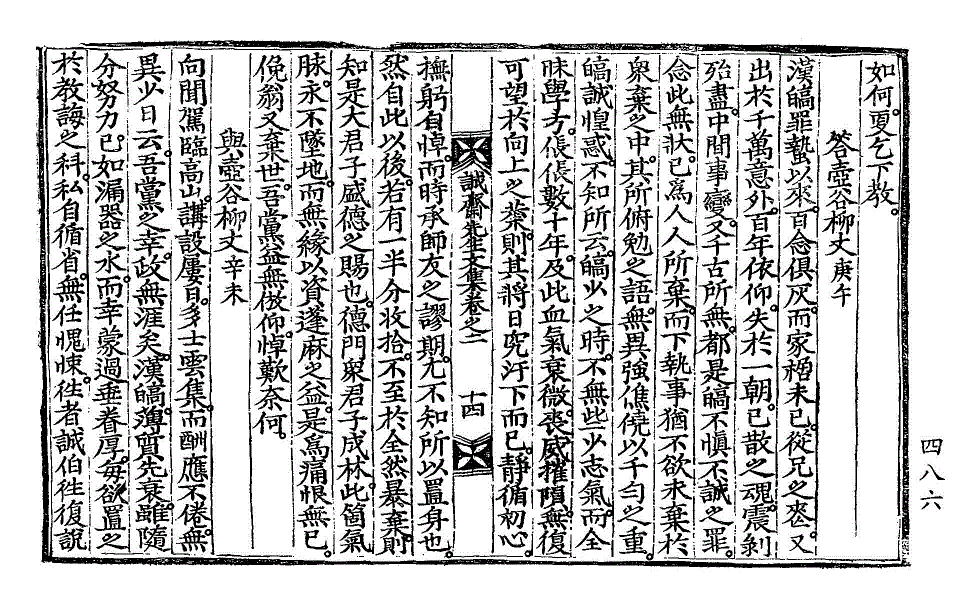 如何。更乞下教。
如何。更乞下教。答壶谷柳丈(庚午)
汉皓罪蛰以来。百念俱灰。而家祸未已。从兄之丧。又出于千万意外。百年依仰。失于一朝。已散之魂。震剥殆尽。中间事变。又千古所无。都是皓不慎不诚之罪。念此无状。已为人人所弃。而下执事犹不欲永弃于众弃之中。其所俯勉之语。无异强僬侥以千匀之重。皓诚惶惑。不知所云。皓少之时。不无些少志气。而全昧学方。伥伥数十年。及此血气衰微。丧威摧陨。无复可望于向上之业。则其将日究污下而已。静循初心。抚躬自悼。而时承师友之谬期。尤不知所以置身也。然自此以后。若有一半分收拾。不至于全然暴弃。则知是大君子盛德之赐也。德门众君子成林。此个气脉。永不坠地。而无缘以资蓬麻之益。是为痛恨无已。俛翁又弃世。吾党益无仿仰。悼叹奈何。
与壶谷柳丈(辛未)
向闻驾临高山。讲设屡日。多士云集。而酬应不倦。无异少日云。吾党之幸。政无涯矣。汉皓。薄质先衰。虽随分努力。已如漏器之水。而幸蒙过垂眷厚。每欲置之于教诲之科。私自循省。无任愧悚。往者诚伯往复说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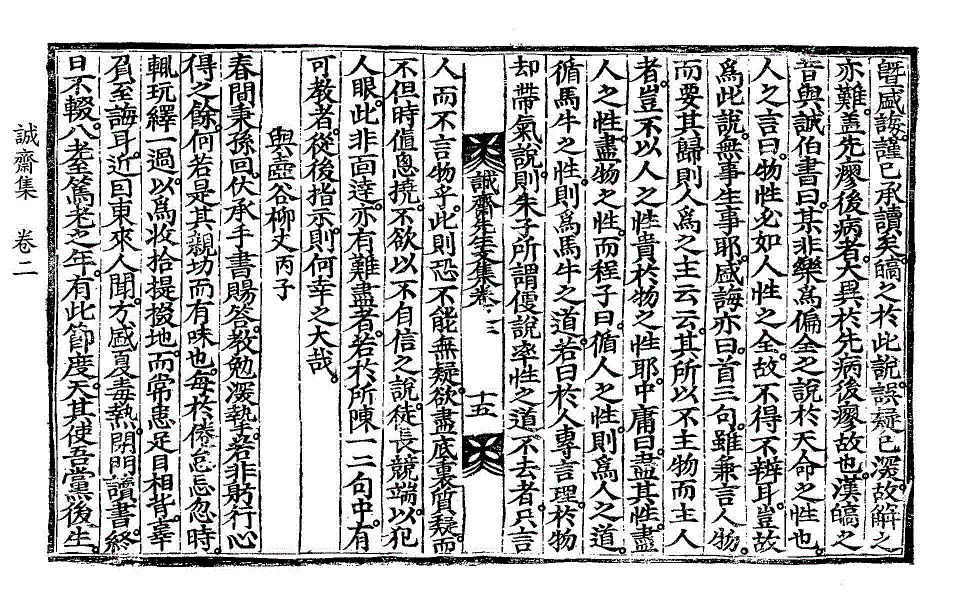 暨盛诲。谨已承读矣。皓之于此说。误疑已深。故解之亦难。盖先瘳后病者。大异于先病后瘳故也。汉皓之昔与诚伯书曰。某非乐为偏全之说于天命之性也。人之言曰。物性必如人性之全。故不得不辨耳。岂故为此说。无事生事耶。盛诲亦曰。首三句。虽兼言人物。而要其归则人为之主云云。其所以不主物而主人者。岂不以人之性贵于物之性耶。中庸曰。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程子曰。循人之性。则为人之道。循马牛之性。则为马牛之道。若曰于人专言理。于物却带气说。则朱子所谓便说率性之道不去者。只言人而不言物乎。此则恐不能无疑。欲尽底里质疑。而不但时值悤挠。不欲以不自信之说。徒长竞端。以犯人眼。此非面达。亦有难尽者。若于所陈一二句中。有可教者。从后指示。则何幸之大哉。
暨盛诲。谨已承读矣。皓之于此说。误疑已深。故解之亦难。盖先瘳后病者。大异于先病后瘳故也。汉皓之昔与诚伯书曰。某非乐为偏全之说于天命之性也。人之言曰。物性必如人性之全。故不得不辨耳。岂故为此说。无事生事耶。盛诲亦曰。首三句。虽兼言人物。而要其归则人为之主云云。其所以不主物而主人者。岂不以人之性贵于物之性耶。中庸曰。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程子曰。循人之性。则为人之道。循马牛之性。则为马牛之道。若曰于人专言理。于物却带气说。则朱子所谓便说率性之道不去者。只言人而不言物乎。此则恐不能无疑。欲尽底里质疑。而不但时值悤挠。不欲以不自信之说。徒长竞端。以犯人眼。此非面达。亦有难尽者。若于所陈一二句中。有可教者。从后指示。则何幸之大哉。与壶谷柳丈(丙子)
春间秉孙回。伏承手书赐答。教勉深挚。若非躬行心得之馀。何若是其亲切而有味也。每于倦怠忘忽时。辄玩绎一过。以为收拾提掇地。而常患足目相背。辜负至诲耳。近因东来人闻。方盛夏毒热。闭门读书。终日不辍。八耋笃老之年。有此节度。天其使吾党后生。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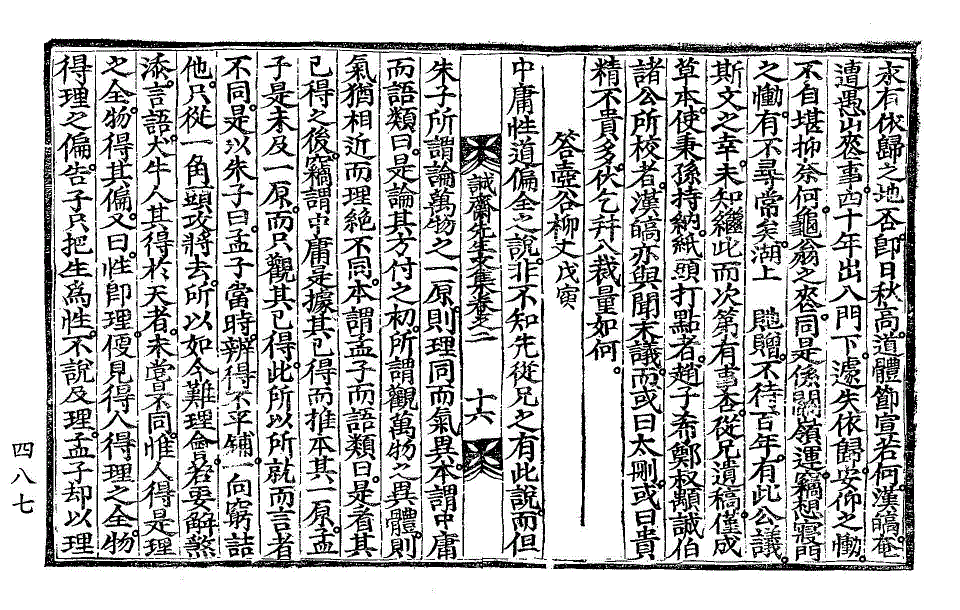 永有依归之地否。即日秋高。道体节宣若何。汉皓。奄遭愚山丧事。四十年出入门下。遽失依归。安仰之恸。不自堪抑奈何。龟翁之丧。同是系关岭运。窃想寝门之恸。有不寻常矣。湖上 貤赠。不待百年。有此公议。斯文之幸。未知继此而次第有事否。从兄遗稿。仅成草本。使秉孙持纳。纸头打点者。赵子希,郑叔颙诚伯诸公所校者。汉皓亦与闻末议。而或曰太删。或曰贵精不贵多。伏乞并入裁量如何。
永有依归之地否。即日秋高。道体节宣若何。汉皓。奄遭愚山丧事。四十年出入门下。遽失依归。安仰之恸。不自堪抑奈何。龟翁之丧。同是系关岭运。窃想寝门之恸。有不寻常矣。湖上 貤赠。不待百年。有此公议。斯文之幸。未知继此而次第有事否。从兄遗稿。仅成草本。使秉孙持纳。纸头打点者。赵子希,郑叔颙诚伯诸公所校者。汉皓亦与闻末议。而或曰太删。或曰贵精不贵多。伏乞并入裁量如何。答壶谷柳丈(戊寅)
中庸性道偏全之说。非不知先从兄之有此说。而但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本谓中庸而语类曰。是论其方付之初。所谓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本谓孟子而语类曰。是看其已得之后。窃谓中庸是据其已得而推本其一原。孟子是未及一原。而只观其已得。此所以所就而言者不同。是以朱子曰。孟子当时。辨得不平铺。一向穷诘他。只从一角头攻将去。所以如今难理会。若要解煞添。言语。犬牛人其得于天者。未尝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其偏。又曰。性即理。便见得人得理之全。物得理之偏。告子只把生为性。不说及理。孟子却以理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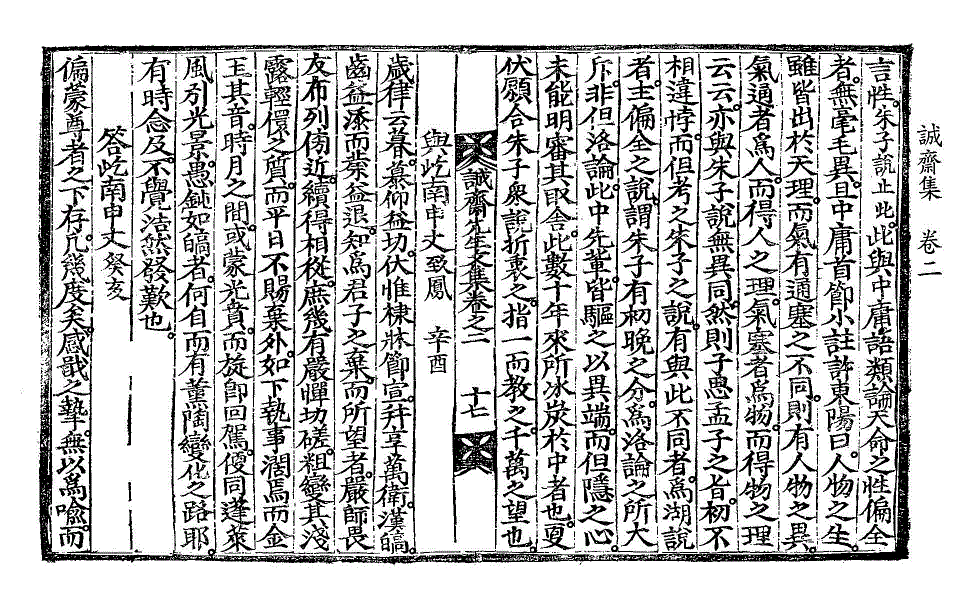 言性。(朱子说止此。)此与中庸,语类论天命之性偏全者。无毫毛异。且中庸首节小注许东阳曰。人物之生。虽皆出于天理。而气有通塞之不同。则有人物之异。气通者为人。而得人之理。气塞者为物。而得物之理云云。亦与朱子说无异同。然则子思孟子之旨。初不相违悖。而但考之朱子之说。有与此不同者。为湖说者。主偏全之说。谓朱子有初晚之分。为洛论之所大斥。非但洛论。此中先辈。皆驱之以异端。而但隐之心。未能明审其取舍。此数十年来所冰炭于中者也。更伏愿合朱子众说折衷之。指一而教之。千万之望也。
言性。(朱子说止此。)此与中庸,语类论天命之性偏全者。无毫毛异。且中庸首节小注许东阳曰。人物之生。虽皆出于天理。而气有通塞之不同。则有人物之异。气通者为人。而得人之理。气塞者为物。而得物之理云云。亦与朱子说无异同。然则子思孟子之旨。初不相违悖。而但考之朱子之说。有与此不同者。为湖说者。主偏全之说。谓朱子有初晚之分。为洛论之所大斥。非但洛论。此中先辈。皆驱之以异端。而但隐之心。未能明审其取舍。此数十年来所冰炭于中者也。更伏愿合朱子众说折衷之。指一而教之。千万之望也。与屹南申丈(致凤○辛酉)
岁律云暮。慕仰益切。伏惟棣床节宣。并享万卫。汉皓。齿益添而业益退。知为君子之弃。而所望者。严师畏友布列傍近。续得相从。庶几有严惮切磋。粗变其浅露轻儇之质。而平日不赐弃外。如下执事阔焉而金玉其音。时月之间。或蒙光贲。而旋即回驾。便同蓬莱风引光景。愚钝如皓者。何自而有薰陶变化之路耶。有时念及。不觉浩然发叹也。
答屹南申丈(癸亥)
偏蒙尊者之下存。凡几度矣。感戢之挚。无以为喻。而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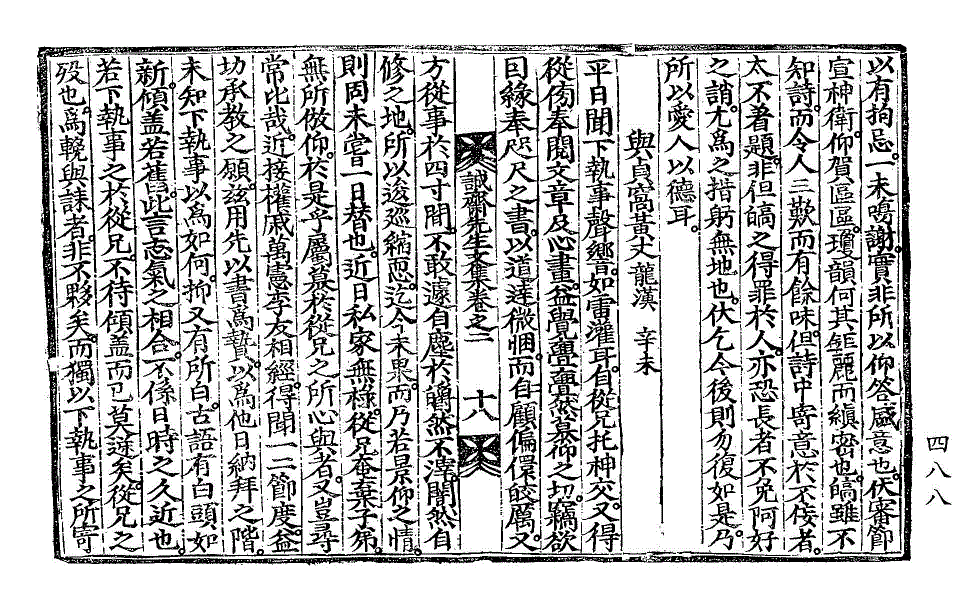 以有拘忌。一未鸣谢。实非所以仰答盛意也。伏审节宣神卫。仰贺区区。琼韵何其钜丽而缜密也。皓虽不知诗。而令人三叹而有馀味。但诗中寄意于不佞者。太不着题。非但皓之得罪于人。亦恐长者不免阿好之诮。尤为之措躬无地也。伏乞今后则勿复如是。乃所以爱人以德耳。
以有拘忌。一未鸣谢。实非所以仰答盛意也。伏审节宣神卫。仰贺区区。琼韵何其钜丽而缜密也。皓虽不知诗。而令人三叹而有馀味。但诗中寄意于不佞者。太不着题。非但皓之得罪于人。亦恐长者不免阿好之诮。尤为之措躬无地也。伏乞今后则勿复如是。乃所以爱人以德耳。与贞窝黄丈(龙汉○辛未)
平日闻下执事声响。如雷灌耳。自从兄托神交。又得从傍奉阅文章及心画。益觉亹亹然慕仰之切。窃欲因缘奉咫尺之书。以道达微悃。而自顾偏儇皎厉。又方从事于四寸间。不敢遽自尘于皭然不滓。闇然自修之地。所以逡巡缩恧。迄今未果。而乃若景仰之情。则固未尝一日替也。近日私家无禄。从兄奄弃子弟。无所仿仰。于是乎属慕于从兄之所心与者。又岂寻常比哉。近接权戚万宪李友相经。得闻一二节度。益切承教之愿。玆用先以书为贽。以为他日纳拜之阶。未知下执事以为如何。抑又有所白。古语有白头如新。倾盖若旧。此言志气之相合。不系日时之久近也。若下执事之于从兄。不待倾盖而已莫逆矣。从兄之殁也。为挽与诔者。非不夥矣。而独以下执事之所寄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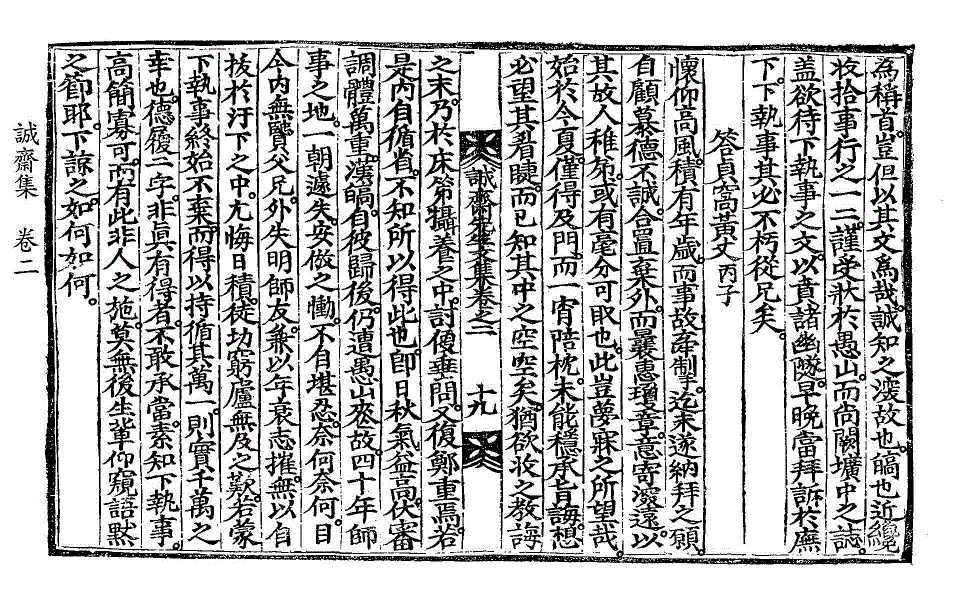 为称首。岂但以其文为哉。诚知之深故也。皓也近才收拾事行之一二。谨受状于愚山。而尚阙圹中之志。盖欲待下执事之文。以贲诸幽隧。早晚当拜诉于庑下。下执事其必不朽从兄矣。
为称首。岂但以其文为哉。诚知之深故也。皓也近才收拾事行之一二。谨受状于愚山。而尚阙圹中之志。盖欲待下执事之文。以贲诸幽隧。早晚当拜诉于庑下。下执事其必不朽从兄矣。答贞窝黄丈(丙子)
怀仰高风。积有年岁。而事故牵掣。迄未遂纳拜之愿。自顾慕德不诚。合置弃外。而曩惠琼章。意寄深远。以其故人稚弟。或有毫分可取也。此岂梦寐之所望哉。始于今夏。仅得及门。而一宵陪枕。未能稳承旨诲。想必望其眉睫。而已知其中之空空矣。犹欲收之教诲之末。乃于床笫摄养之中。讨便垂问。又复郑重焉。若是内自循省。不知所以得此也。即日秋气益高。伏审调体万重。汉皓。自彼归后。仍遭愚山丧故。四十年师事之地。一朝遽失。安仿之恸。不自堪忍。奈何奈何。目今内无贤父兄。外失明师友。兼以年衰志摧。无以自拔于污下之中。尤悔日积。徒切穷庐无及之叹。若蒙下执事终始不弃。而得以持循其万一。则实千万之幸也。德履二字。非真有得者。不敢承当。素知下执事。高简寡可。而有此非人之施。莫无后生辈仰窥语默之节耶。下谅之。如何如何。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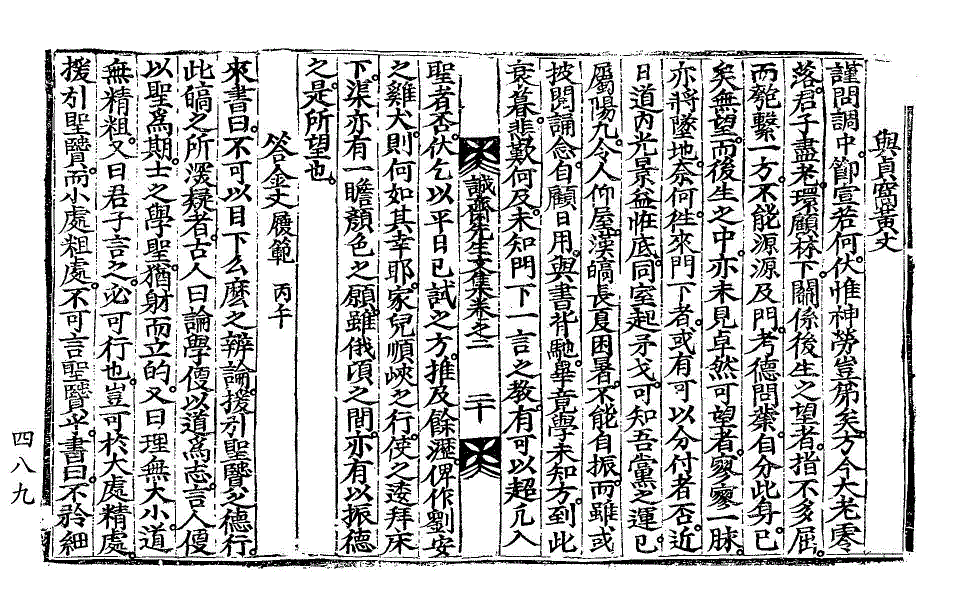 与贞窝黄丈
与贞窝黄丈谨问调中。节宣若何。伏惟神劳岂弟矣。方今大老零落。君子尽老。环顾林下。关系后生之望者。指不多屈。而匏系一方。不能源源及门。考德问业。自分此身。已矣无望。而后生之中。亦未见卓然可望者。寥寥一脉。亦将坠地。奈何。往来门下者。或有可以分付者否。近日道内光景益怪底。同室起矛戈。可知吾党之运。已属阳九。令人仰屋。汉皓长夏困暑。不能自振。而虽或披阅诵念。自顾日用。与书背驰。毕竟学未知方。到此衰暮。悲叹何及。未知门下一言之教。有可以超凡入圣者否。伏乞以平日已试之方。推及馀沥。俾作刘安之鸡犬。则何如其幸耶。家儿顺峡之行。使之逶拜床下。渠亦有一瞻颜色之愿。虽俄顷之间。亦有以振德之。是所望也。
答金丈(履范○丙午)
来书曰。不可以目下幺么之辨论。援引圣贤之德行。此皓之所深疑者。古人曰论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期。士之学圣。犹射而立的。又曰理无大小。道无精粗。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岂可于大处精处。援引圣贤。而小处粗处。不可言圣贤乎。书曰。不矜细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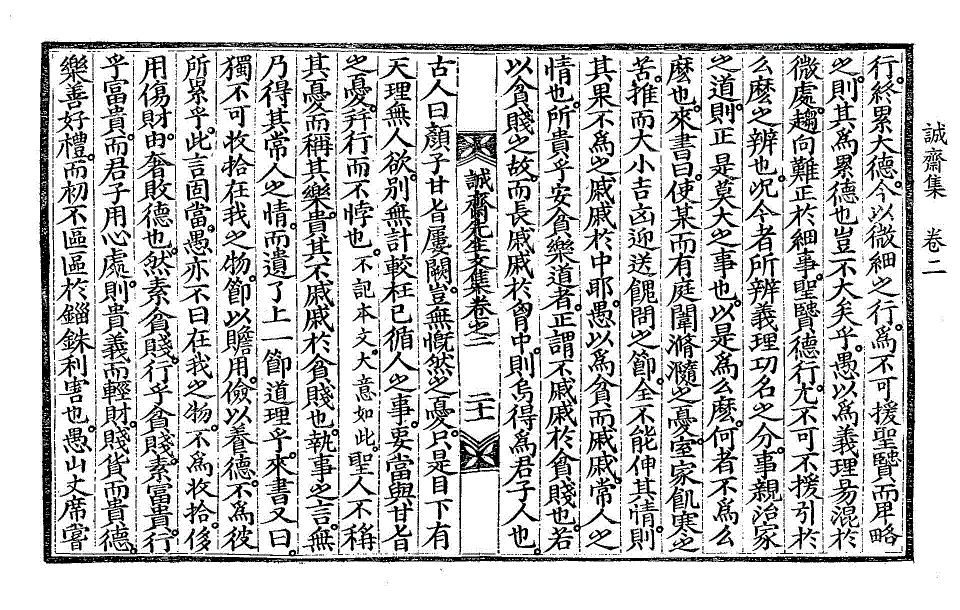 行。终累大德。今以微细之行。为不可援圣贤而卑略之。则其为累德也岂不大矣乎。愚以为义理易混于微处。趋向难正于细事。圣贤德行。尤不可不援引于幺么之辨也。况今者所辨义理功名之分。事亲治家之道。则正是莫大之事也。以是为幺么。何者不为幺么也。来书曰。使某而有庭闱滫瀡之忧。室家饥寒之苦。推而大小吉凶迎送馈问之节。全不能伸其情。则其果不为之戚戚于中耶。愚以为贫而戚戚。常人之情也。所贵乎安贫乐道者。正谓不戚戚于贫贱也。若以贫贱之故。而长戚戚于胸中。则乌得为君子人也。古人曰颜子甘旨屡阙。岂无慨然之忧。只是目下有天理无人欲。别无计较枉己循人之事。要当与甘旨之忧。并行而不悖也。(不记本文。大意如此。)圣人不称其忧而称其乐。贵其不戚戚于贫贱也。执事之言。无乃得其常人之情。而遗了上一节道理乎。来书又曰。独不可收拾在我之物。节以赡用。俭以养德。不为彼所累乎。此言固当。愚亦不曰在我之物。不为收拾。侈用伤财。由奢败德也。然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而君子用心处。则贵义而轻财。贱货而贵德。乐善好礼。而初不区区于锱铢利害也。愚山丈席尝
行。终累大德。今以微细之行。为不可援圣贤而卑略之。则其为累德也岂不大矣乎。愚以为义理易混于微处。趋向难正于细事。圣贤德行。尤不可不援引于幺么之辨也。况今者所辨义理功名之分。事亲治家之道。则正是莫大之事也。以是为幺么。何者不为幺么也。来书曰。使某而有庭闱滫瀡之忧。室家饥寒之苦。推而大小吉凶迎送馈问之节。全不能伸其情。则其果不为之戚戚于中耶。愚以为贫而戚戚。常人之情也。所贵乎安贫乐道者。正谓不戚戚于贫贱也。若以贫贱之故。而长戚戚于胸中。则乌得为君子人也。古人曰颜子甘旨屡阙。岂无慨然之忧。只是目下有天理无人欲。别无计较枉己循人之事。要当与甘旨之忧。并行而不悖也。(不记本文。大意如此。)圣人不称其忧而称其乐。贵其不戚戚于贫贱也。执事之言。无乃得其常人之情。而遗了上一节道理乎。来书又曰。独不可收拾在我之物。节以赡用。俭以养德。不为彼所累乎。此言固当。愚亦不曰在我之物。不为收拾。侈用伤财。由奢败德也。然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而君子用心处。则贵义而轻财。贱货而贵德。乐善好礼。而初不区区于锱铢利害也。愚山丈席尝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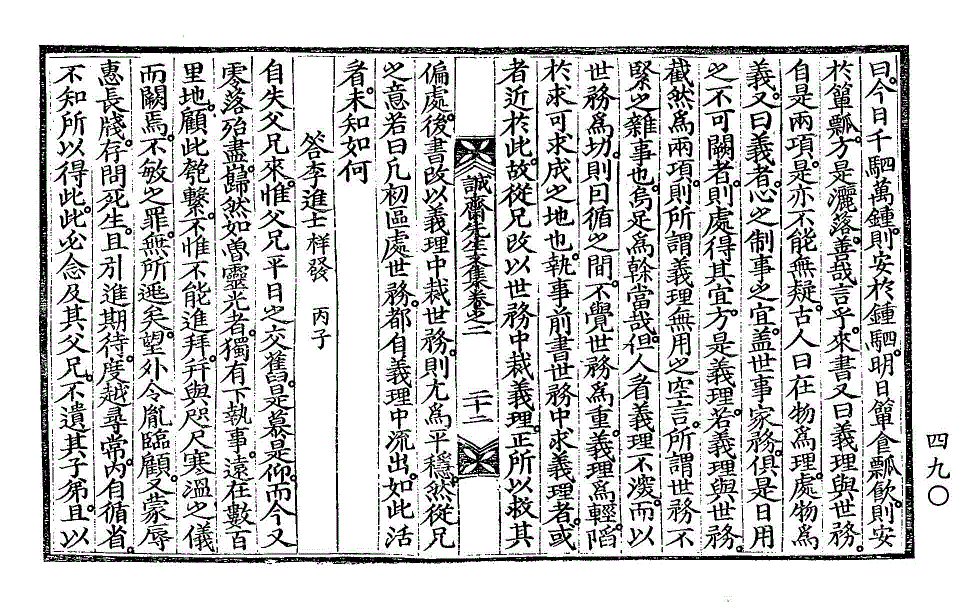 曰。今日千驷万钟。则安于钟驷。明日箪食瓢饮。则安于箪瓢。方是洒落。善哉言乎。来书又曰义理与世务。自是两项。是亦不能无疑。古人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盖世事家务。俱是日用之不可阙者。则处得其宜。方是义理。若义理与世务。截然为两项。则所谓义理无用之空言。所谓世务不紧之杂事也。乌足为干当哉。但人看义理不深。而以世务为切。则因循之间。不觉世务为重。义理为轻。陷于求可求成之地也。执事前书世务中求义理者。或者近于此。故从兄改以世务中裁义理。正所以救其偏处。后书改以义理中裁世务。则尤为平稳。然从兄之意若曰凡初区处世务。都自义理中流出。如此活看。未知如何。
曰。今日千驷万钟。则安于钟驷。明日箪食瓢饮。则安于箪瓢。方是洒落。善哉言乎。来书又曰义理与世务。自是两项。是亦不能无疑。古人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盖世事家务。俱是日用之不可阙者。则处得其宜。方是义理。若义理与世务。截然为两项。则所谓义理无用之空言。所谓世务不紧之杂事也。乌足为干当哉。但人看义理不深。而以世务为切。则因循之间。不觉世务为重。义理为轻。陷于求可求成之地也。执事前书世务中求义理者。或者近于此。故从兄改以世务中裁义理。正所以救其偏处。后书改以义理中裁世务。则尤为平稳。然从兄之意若曰凡初区处世务。都自义理中流出。如此活看。未知如何。答李进士(祥发○丙子)
自失父兄来。惟父兄平日之交旧。是慕是仰。而今又零落殆尽。岿然如鲁灵光者。独有下执事。远在数百里地。顾此匏系。不惟不能进拜。并与咫尺寒温之仪而阙焉。不敏之罪。无所逃矣。望外令胤临顾。又蒙辱惠长笺。存问死生。且引进期待。度越寻常。内自循省。不知所以得此。此必念及其父兄。不遗其子弟。且以
诚斋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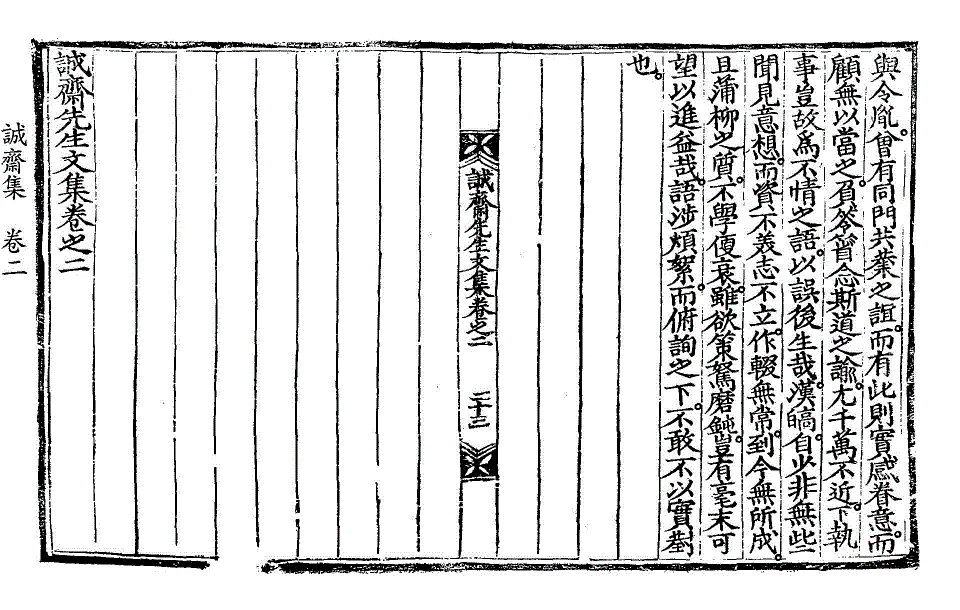 与令胤。曾有同门共业之谊。而有比则实感眷意。而顾无以当之。负笭箵念斯道之谕。尤千万不近。下执事岂故为不情之语。以误后生哉。汉皓。自少非无些闻见意想。而资不美志不立。作辍无常。到今无所成。且蒲柳之质。不学便衰。虽欲策驽磨钝。岂有毫末可望以进益哉。语涉烦絮。而俯询之下。不敢不以实对也。
与令胤。曾有同门共业之谊。而有比则实感眷意。而顾无以当之。负笭箵念斯道之谕。尤千万不近。下执事岂故为不情之语。以误后生哉。汉皓。自少非无些闻见意想。而资不美志不立。作辍无常。到今无所成。且蒲柳之质。不学便衰。虽欲策驽磨钝。岂有毫末可望以进益哉。语涉烦絮。而俯询之下。不敢不以实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