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x 页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赋
赋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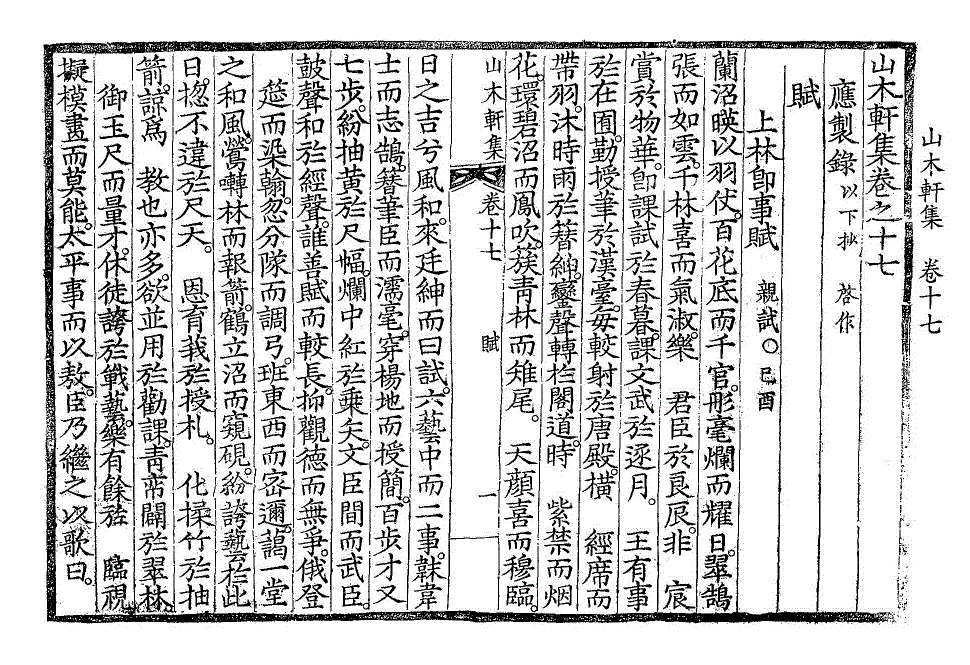 上林即事赋(亲试○己酉)
上林即事赋(亲试○己酉)兰沼映以羽仗。百花底而千官。彤毫烂而耀日。翠鹄张而如云。千林喜而气淑。乐 君臣于良辰。非 宸赏于物华。即课试于春暮。课文武于逐月。 王有事于在囿。勤授笔于汉台。每较射于唐殿。横 经席而带羽。沐时雨于簪绅。銮声转于阁道。时 紫禁而烟花。环碧沼而凤吹。簇青林而雉尾。 天颜喜而穆临。日之吉兮风和。来廷绅而曰试。六艺中而二事。韎韦士而志鹄。簪笔臣而濡毫。穿杨地而授简。百步才又七步。纷抽黄于尺幅。烂中红于乘矢。文臣间而武臣。鼓声和于经声。谁善赋而较长。抑观德而无争。俄登 筵而染翰。忽分队而调弓。班东西而密迩。蔼一堂之和风。莺啭林而报箭。鹤立沼而窥砚。纷誇艺于此日。揔不违于尺天。 恩育莪于授札。 化揉竹于抽箭。谅为 教也亦多。欲并用于劝课。青帟辟于翠林。 御玉尺而量才。休徒誇于战艺。乐有馀于 临视。拟模画而莫能。太平事而以敖。臣乃继之以歌曰。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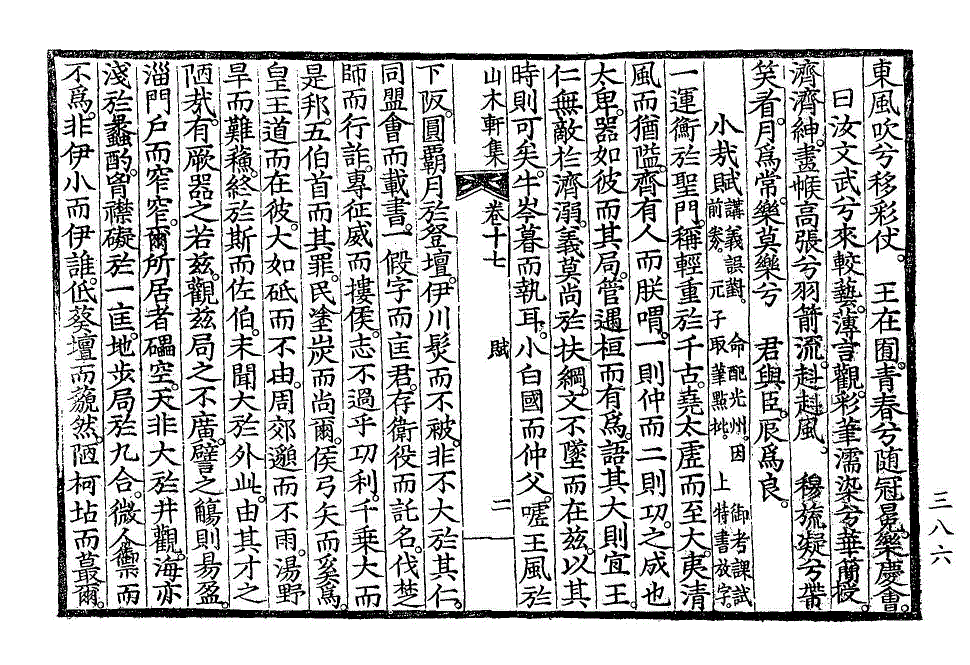 东风吹兮移彩仗。 王在囿。青春兮随冠冕。乐庆会。 曰汝文武兮来较艺。薄言观。彩笔濡染兮华简授。济济绅。画帿高张兮羽箭流。赳赳风。 穆旒凝兮带笑看。月为常。乐莫乐兮 君与臣。辰为良。
东风吹兮移彩仗。 王在囿。青春兮随冠冕。乐庆会。 曰汝文武兮来较艺。薄言观。彩笔濡染兮华简授。济济绅。画帿高张兮羽箭流。赳赳风。 穆旒凝兮带笑看。月为常。乐莫乐兮 君与臣。辰为良。小哉赋(讲义误对。 命配光州。因 御考课试前券。 元子取笔点批。 上特书放字。)
一运衡于圣门。称轻重于千古。尧太虚而至大。夷清风而犹隘。齐有人而朕喟。一则仲而二则功。之成也太卑。器如彼而其局。管遇桓而有为。语其大则宜王。仁无敌于济溺。义莫尚于扶纲。文不坠而在玆。以其时则可矣。牛岑暮而执耳。小白国而仲父。嘘王风于下阪。圆霸月于登坛。伊川发而不被。非不大于其仁。同盟会而载书。一假字而匡君。存卫役而托名。伐楚师而行诈。专征威而楼侯。志不过乎功利。千乘大而是邦。五伯首而其罪。民涂炭而尚尔。侯弓矢而奚为。皇王道而在彼。大如砥而不由。周郊邈而不雨。汤野旱而难苏。终于斯而佐伯。未闻大于外此。由其才之陋哉。有厥器之若玆。观玆局之不广。譬之觞则易盈。淄门户而窄窄。尔所居者礧空。天非大于井观。海亦浅于蠡酌。胸襟碍于一匡。地步局于九合。微人御而不为。非伊小而伊谁。低葵坛而藐然。陋柯坫而蕞尔。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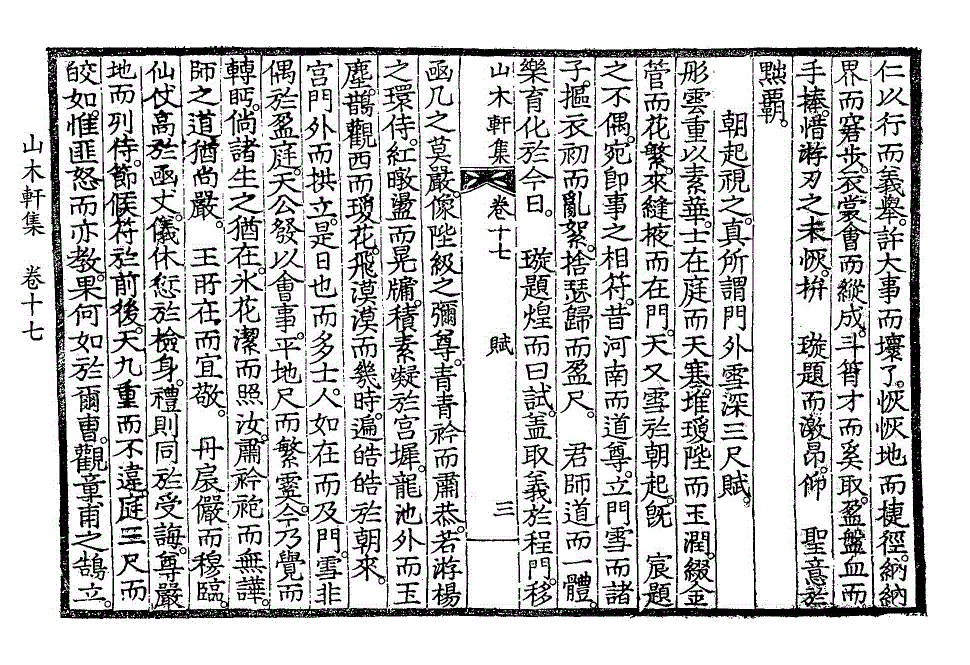 仁以行而义举。许大事而坏了。恢恢地而捷径。纳纳界而窘步。衣裳会而纵成。斗筲才而奚取。盈盘血而手捧。惜游刃之未恢。拚 璇题而激昂。仰 圣意于黜霸。
仁以行而义举。许大事而坏了。恢恢地而捷径。纳纳界而窘步。衣裳会而纵成。斗筲才而奚取。盈盘血而手捧。惜游刃之未恢。拚 璇题而激昂。仰 圣意于黜霸。朝起视之。真所谓门外雪深三尺赋。
彤云重以素华。士在庭而天寒。堆琼陛而玉润。缀金管而花繁。来缝掖而在门。天又雪于朝起。既 宸题之不偶。宛即事之相符。昔河南而道尊。立门雪而诸子。抠衣初而乱絮。舍瑟归而盈尺。 君师道而一体。乐育化于今日。 璇题煌而曰试。盖取义于程门。移函几之莫严。像陛级之弥尊。青青衿而肃恭。若游杨之环侍。红暾荡而晃牖。积素凝于宫墀。龙池外而玉尘。鹊观西而琼花。飞漠漠而几时。遍皓皓于朝来。 宫门外而拱立。是日也而多士。人如在而及门。雪非偶于盈庭。天公发以会事。平地尺而繁霙。今乃觉而转眄。倘诸生之犹在。冰花洁而照汝。肃衿袍而无哗。师之道犹尚严。 王所在而宜敬。 丹扆俨而穆临。仙仗高于函丈。仪休愆于检身。礼则同于受诲。尊严地而列侍。节候符于前后。天九重而不违。庭三尺而皎如。惟匪怒而亦教。果何如于尔曹。观章甫之鹄立。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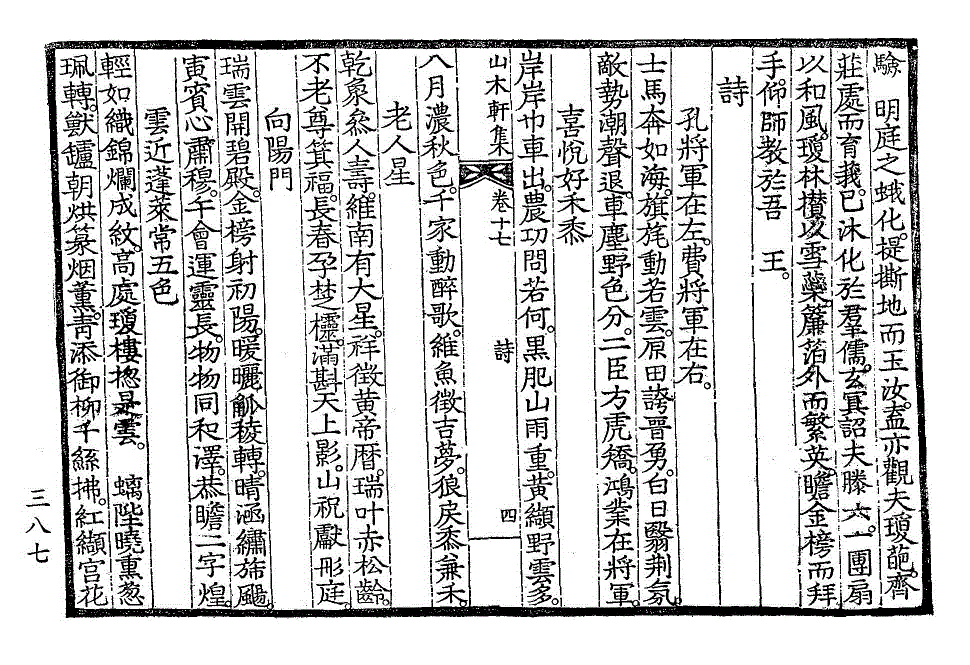 验 明庭之蛾化。提撕地而玉汝。盍亦观夫琼葩。齐庄处而育莪。已沐化于群儒。玄冥诏夫滕六。一团扇以和风。琼林攒以雪蕊。帘箔外而繁英。瞻金榜而拜手。仰师教于吾 王。
验 明庭之蛾化。提撕地而玉汝。盍亦观夫琼葩。齐庄处而育莪。已沐化于群儒。玄冥诏夫滕六。一团扇以和风。琼林攒以雪蕊。帘箔外而繁英。瞻金榜而拜手。仰师教于吾 王。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诗
孔将军在左。费将军在右。
士马奔如海。旗旄动若云。原田誇晋勇。白日翳荆氛。敌势潮声退。车尘野色分。二臣方虎矫。鸿业在将军。
喜悦好禾黍
岸岸巾车出。农功问若何。黑肥山雨重。黄缬野云多。八月浓秋色。千家动醉歌。维鱼徵吉梦。狼戾黍兼禾。
老人星
乾象参人寿。维南有大星。祥徵黄帝历。瑞叶赤松龄。不老尊箕福。长春孕楚棂。满斟天上影。山祝献彤庭。
向阳门
瑞云开碧殿。金榜射初阳。暖晒觚棱转。晴涵绣旆飏。寅宾心肃穆。午会运灵长。物物同和泽。恭瞻二字煌。
云近蓬莱常五色
轻如织锦烂成纹。高处琼楼揔是云。 螭陛晓熏葱佩转。兽垆朝烘篆烟薰。青添御柳千丝拂。红缬宫花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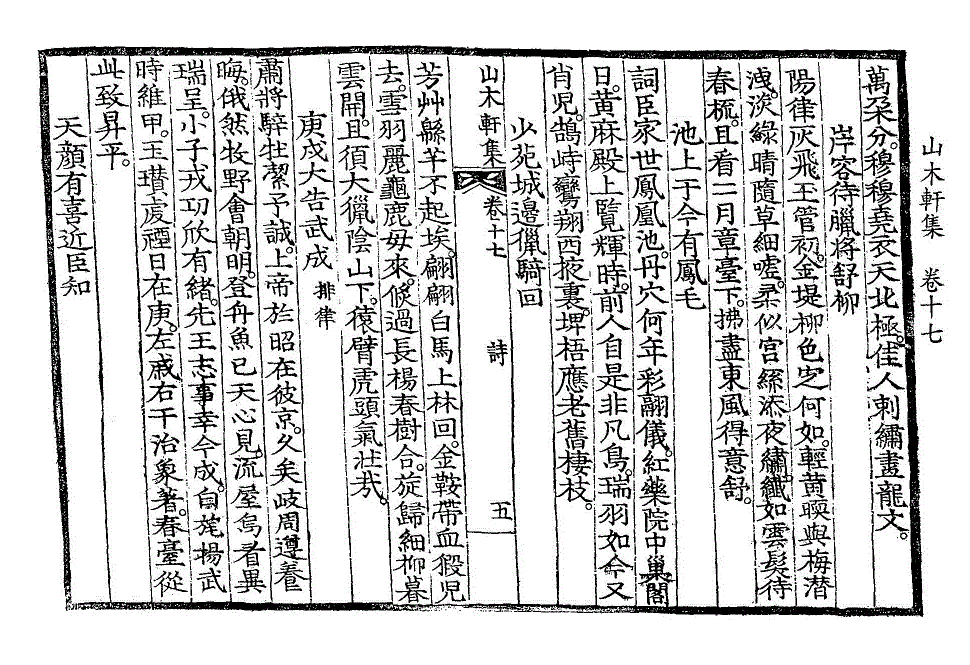 万朵分。穆穆尧衣天北极。佳人刺绣画龙文。
万朵分。穆穆尧衣天北极。佳人刺绣画龙文。岸容待腊将舒柳
阳律灰飞玉管初。金堤柳色定何如。轻黄暖与梅潜泄。淡绿晴随草细嘘。柔似宫丝添夜绣。纤如云发待春梳。且看二月章台下。拂尽东风得意舒。
池上于今有凤毛
词臣家世凤凰池。丹穴何年彩翮仪。红药院中巢阁日。黄麻殿上览辉时。前人自是非凡鸟。瑞羽如今又肖儿。鹄峙鸾翔西掖里。埤梧应老旧栖枝。
少苑城边猎骑回
芳草绵芊不起埃。翩翩白马上林回。金鞍带血猳儿去。雪羽丽龟鹿母来。倏过长杨春树合。旋归细柳暮云开。且须大猎阴山下。猿臂虎头气壮哉。
庚戌大告武成(排律)
肃将骍牡洁予诚。上帝于昭在彼京。久矣岐周遵养晦。俄然牧野会朝明。登舟鱼已天心见。流屋乌看异瑞呈。小子戎功欣有绪。先王志事幸今成。白旄扬武时维甲。玉瓒虔禋日在庚。左戚右干治象著。春台从此致升平。
天颜有喜近臣知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8L 页
 端笏峨冠拜玉墀。薰琴一曲太平词。祥光暖与红云合。和气融成淑景迟。春解龙颜瞻密迩。天临鹓列独恩私。几年掌翰朝青琐。万国无忧验彩眉。满袖香烟携五夜。绕鳞祥日识多时。正逢紫极风云会。又是青春剑佩随。芍药帘㫌仙漏近。芙蓉殿角午阴移。回看法座阳和遍。已觉凝旒玉色怡。瑞旭昭森龙衮袖。恩波洋溢凤凰池。手中五色丝纶字。自幸明时荷圣知。
端笏峨冠拜玉墀。薰琴一曲太平词。祥光暖与红云合。和气融成淑景迟。春解龙颜瞻密迩。天临鹓列独恩私。几年掌翰朝青琐。万国无忧验彩眉。满袖香烟携五夜。绕鳞祥日识多时。正逢紫极风云会。又是青春剑佩随。芍药帘㫌仙漏近。芙蓉殿角午阴移。回看法座阳和遍。已觉凝旒玉色怡。瑞旭昭森龙衮袖。恩波洋溢凤凰池。手中五色丝纶字。自幸明时荷圣知。迎日推筴
冬至阳生七日期。郊天坛下拜云师。一轮瑞旭寅宾地。万户潜雷子建时。叶律阴阳玄象远。周天轨躅大鸿知。观于是日迎黄道。卜以中庭产翠蓍。历数三元仍大衍。分成再扐更归奇。鸿濛辟后三千甲。蚁磨盘中十二支。细玩四方馀一度。几回三百六旬期。测圭功并星台奏。应律时同嶰竹吹。阳至朔朝观复始。天心子夜验无移。请看黄帝绵千历。气数曾从这里推。
金刚一万二千峰
如来现法十方游。幻化金身此地留。海外三千高丽国。人间第一歇惺楼。高低大小诸山合。南北东西万景稠。闪铄黄金飞百道。虚明白玉竞千流。云归须弥苍苍面。日映毗卢上上头。千佛尊严疑卓锡。群仙飞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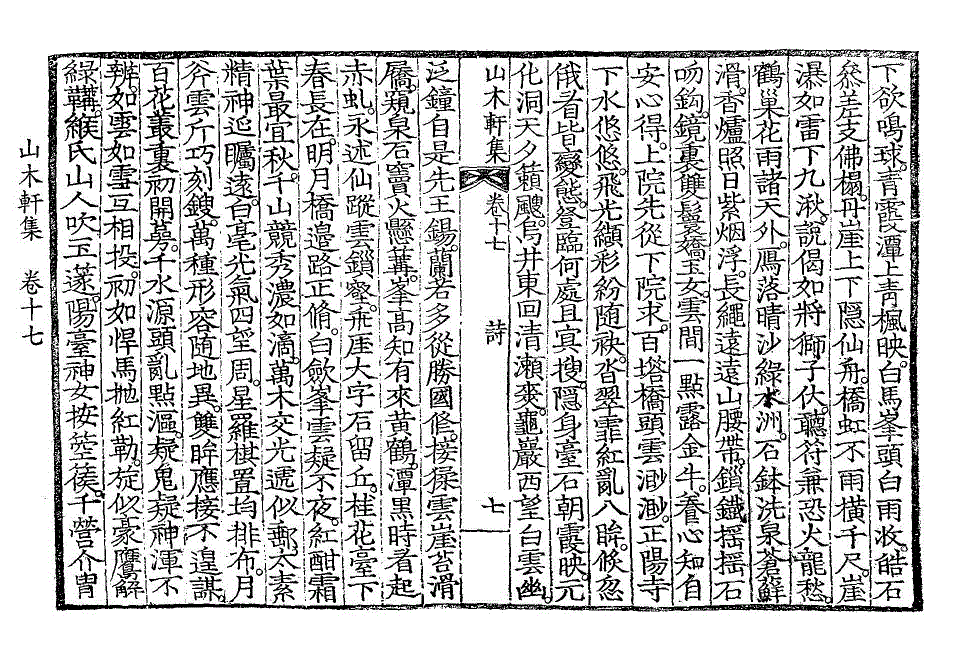 下欲鸣球。青霞潭上青枫映。白马峰头白雨收。皓石参差支佛榻。丹崖上下隐仙舟。桥虹不雨横千尺。崖瀑如雷下九湫。说偈如将狮子伏。听符兼恐火龙愁。鹤巢花雨诸天外。雁落晴沙绿水洲。石钵洗泉苍藓滑。香炉照日紫烟浮。长绳远远山腰带。锁铁摇摇石吻钩。镜里双鬟娇玉女。云间一点露金牛。养心知自安心得。上院先从下院求。百塔桥头云渺渺。正阳寺下水悠悠。飞光缬彩纷随袂。沓翠霏红乱入眸。倏忽俄看皆变态。登临何处且冥搜。隐身台石朝霞映。元化洞天夕籁飕。乌井东回清濑爽。龟岩西望白云幽。泛钟自是先王锡。兰若多从胜国修。接猱云崖苔滑屩。窥泉石窦火悬篝。峰高知有来黄鹤。潭黑时看起赤虬。永述仙踪云锁壑。乖厓大字石留丘。桂花台下春长在。明月桥边路正脩。白敛峰云疑不夜。红酣霜叶最宜秋。千山竞秀浓如滴。万木交光递似邮。太素精神延瞩远。白毫光气四望周。星罗棋置均排布。月斧云斤巧刻锼。万种形容随地异。双眸应接不遑谋。百花丛里初开萼。千水源头乱点沤。疑鬼疑神浑不辨。如云如雪互相投。初如悍马抛红勒。旋似豪鹰解绿鞲。缑氏山人吹玉篴。阳台神女按箜篌。千营介冑
下欲鸣球。青霞潭上青枫映。白马峰头白雨收。皓石参差支佛榻。丹崖上下隐仙舟。桥虹不雨横千尺。崖瀑如雷下九湫。说偈如将狮子伏。听符兼恐火龙愁。鹤巢花雨诸天外。雁落晴沙绿水洲。石钵洗泉苍藓滑。香炉照日紫烟浮。长绳远远山腰带。锁铁摇摇石吻钩。镜里双鬟娇玉女。云间一点露金牛。养心知自安心得。上院先从下院求。百塔桥头云渺渺。正阳寺下水悠悠。飞光缬彩纷随袂。沓翠霏红乱入眸。倏忽俄看皆变态。登临何处且冥搜。隐身台石朝霞映。元化洞天夕籁飕。乌井东回清濑爽。龟岩西望白云幽。泛钟自是先王锡。兰若多从胜国修。接猱云崖苔滑屩。窥泉石窦火悬篝。峰高知有来黄鹤。潭黑时看起赤虬。永述仙踪云锁壑。乖厓大字石留丘。桂花台下春长在。明月桥边路正脩。白敛峰云疑不夜。红酣霜叶最宜秋。千山竞秀浓如滴。万木交光递似邮。太素精神延瞩远。白毫光气四望周。星罗棋置均排布。月斧云斤巧刻锼。万种形容随地异。双眸应接不遑谋。百花丛里初开萼。千水源头乱点沤。疑鬼疑神浑不辨。如云如雪互相投。初如悍马抛红勒。旋似豪鹰解绿鞲。缑氏山人吹玉篴。阳台神女按箜篌。千营介冑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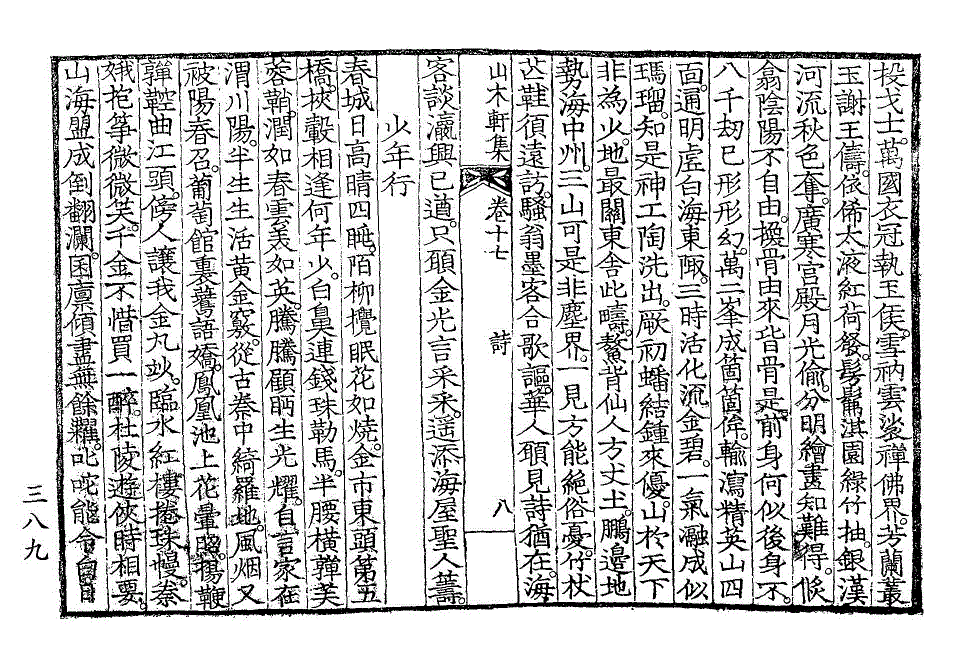 投戈士。万国衣冠执玉侯。雪衲云裟禅佛界。芳兰丛玉谢王俦。依俙太液红荷发。髣髴淇园绿竹抽。银汉河流秋色夺。广寒宫殿月光偷。分明绘画知难得。倏翕阴阳不自由。换骨由来皆骨是。前身何似后身不。八千劫已形形幻。万二峰成个个侔。输泻精英山四面。通明虚白海东陬。三时活化流金碧。一气融成似玛琉。知是神工陶洗出。厥初蟠结钟来优。山于天下非为少。地最关东舍此畴。鳌背仙人方丈土。鹏边地势海中州。三山可是非尘界。一见方能绝俗忧。竹杖芒鞋须远访。骚翁墨客合歌讴。华人愿见诗犹在。海客谈瀛兴已遒。只愿金光言采采。遥添海屋圣人筹。
投戈士。万国衣冠执玉侯。雪衲云裟禅佛界。芳兰丛玉谢王俦。依俙太液红荷发。髣髴淇园绿竹抽。银汉河流秋色夺。广寒宫殿月光偷。分明绘画知难得。倏翕阴阳不自由。换骨由来皆骨是。前身何似后身不。八千劫已形形幻。万二峰成个个侔。输泻精英山四面。通明虚白海东陬。三时活化流金碧。一气融成似玛琉。知是神工陶洗出。厥初蟠结钟来优。山于天下非为少。地最关东舍此畴。鳌背仙人方丈土。鹏边地势海中州。三山可是非尘界。一见方能绝俗忧。竹杖芒鞋须远访。骚翁墨客合歌讴。华人愿见诗犹在。海客谈瀛兴已遒。只愿金光言采采。遥添海屋圣人筹。少年行
春城日高晴四眺。陌柳搅眠花如烧。金市东头第五桥。挟毂相逢何年少。白鼻连钱珠勒马。半腰横亸芙蓉鞘。润如春云美如英。腾腾顾眄生光耀。自言家在渭川阳。半生生活黄金窍。从古秦中绮罗地。风烟又被阳春召。葡萄馆里燕语娇。凤凰池上花晕照。扬鞭亸鞚曲江头。傍人让我金丸妙。临水红楼捲珠幔。秦娥抱筝微微笑。千金不惜买一醉。杜陵游侠时相要。山海盟成倒翻澜。囷廪倾尽无馀粜。叱咜能令白日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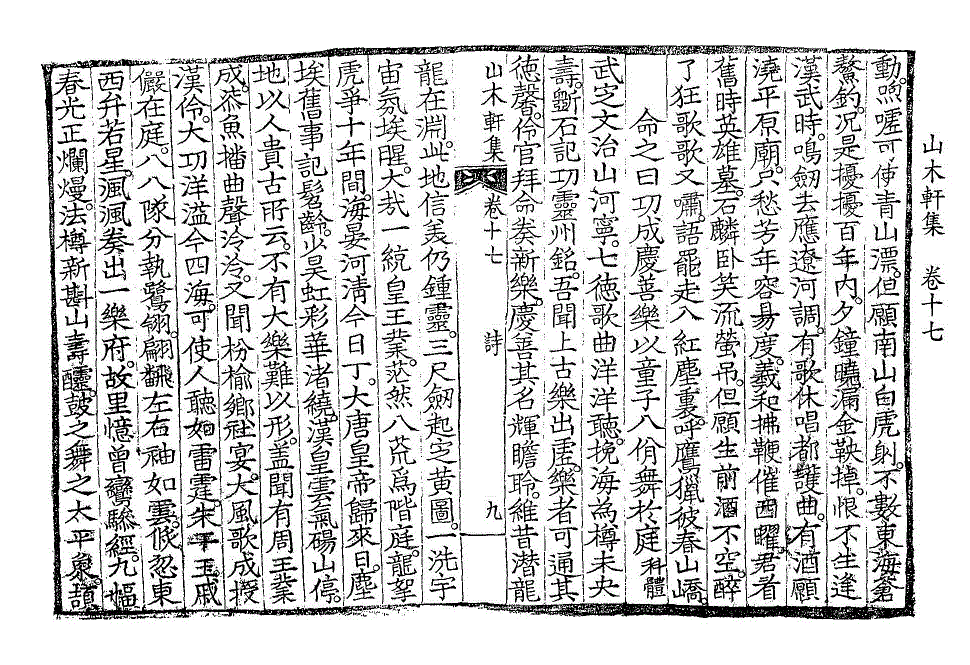 动。喣嘘可使青山漂。但愿南山白虎射。不数东海苍鳌钓。况是扰扰百年内。夕钟晓漏金鞅掉。恨不生逢汉武时。鸣剑去应辽河调。有歌休唱都护曲。有酒愿浇平原庙。只愁芳年容易度。羲和拂鞭催西曜。君看旧时英雄墓。石麟卧笑流萤吊。但愿生前酒不空。醉了狂歌歌又啸。语罢走入红尘里。呼鹰猎彼春山峤。
动。喣嘘可使青山漂。但愿南山白虎射。不数东海苍鳌钓。况是扰扰百年内。夕钟晓漏金鞅掉。恨不生逢汉武时。鸣剑去应辽河调。有歌休唱都护曲。有酒愿浇平原庙。只愁芳年容易度。羲和拂鞭催西曜。君看旧时英雄墓。石麟卧笑流萤吊。但愿生前酒不空。醉了狂歌歌又啸。语罢走入红尘里。呼鹰猎彼春山峤。命之曰功成庆善乐以童子八佾舞于庭(科体)
武定文治山河宁。七德歌曲洋洋听。挽海为樽未央寿。斲石记功灵州铭。吾闻上古乐出虚。乐者可通其德馨。伶官拜命奏新乐。庆善其名辉瞻聆。维昔潜龙龙在渊。此地信美仍钟灵。三尺剑起定黄图。一洗宇宙氛埃腥。大哉一统皇王业。茫然八荒为阶庭。龙挐虎争十年间。海晏河清今日丁。大唐皇帝归来日。尘埃旧事记髫龄。少昊虹彩华渚绕。汉皇云气砀山停。地以人贵古所云。不有大乐难以形。盖闻有周王业成。㓒鱼播曲声泠泠。又闻枌榆乡社宴。大风歌成授汉伶。大功洋溢今四海。可使人听如雷霆。朱干玉戚俨在庭。八八队分执鹭翎。翩翻左右袖如云。倏忽东西弁若星。沨沨奏出一乐府。故里忆曾鸾骖经。九幅春光正烂熳。法樽新斟山寿𨤍。鼓之舞之太平象。颉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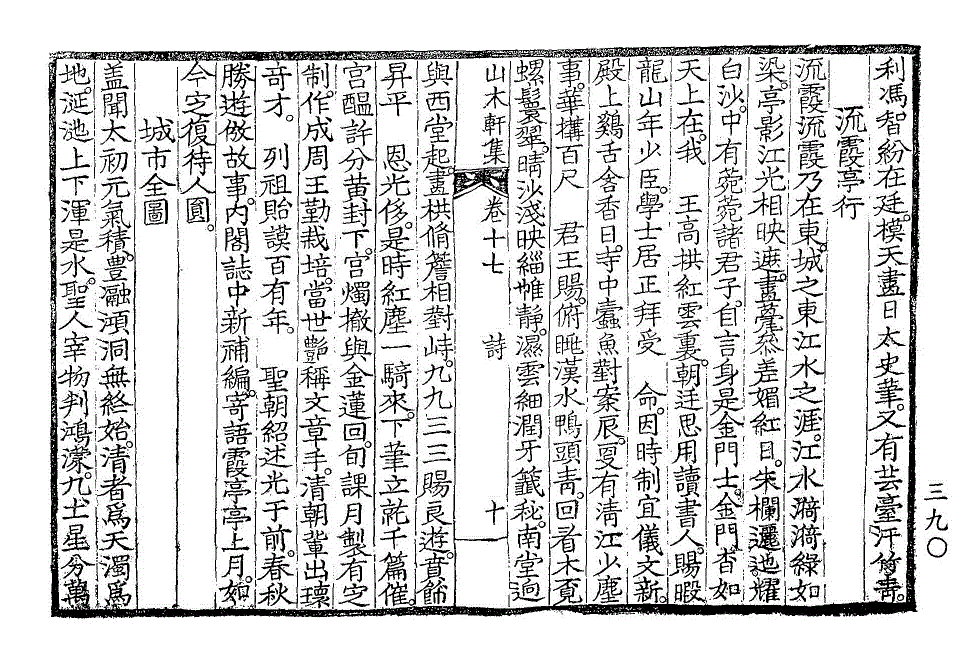 利冯智纷在廷。模天画日太史笔。又有芸台汗竹青。
利冯智纷在廷。模天画日太史笔。又有芸台汗竹青。流霞亭行
流霞流霞乃在东。城之东江水之涯。江水漪漪绿如染。亭影江光相映遮。画甍参差媚红日。朱栏逦迤耀白沙。中有菀菀诸君子。自言身是金门士。金门杳如天上在。我 王高拱红云里。朝廷思用读书人。赐暇龙山年少臣。学士居正拜受 命。因时制宜仪文新。殿上鸡舌含香日。寺中蠹鱼对案辰。更有清江少尘事。华搆百尺 君王赐。俯眺汉水鸭头青。回看木觅螺鬟翠。晴沙浅映缁帷静。湿云细润牙签秘。南堂迥与西堂起。画栱脩檐相对峙。九九三三赐良游。贲饰升平 恩光侈。是时红尘一骑来。下笔立就千篇催。宫酝许分黄封下。宫烛撤与金莲回。旬课月制有定制。作成周王勤栽培。当世艳称文章手。清朝辈出瑰奇才。 列祖贻谟百有年。 圣朝绍述光于前。春秋胜游仿故事。内阁志中新补编。寄语霞亭亭上月。如今定复待人圆。
城市全图
盖闻太初元气积。礼融澒洞无终始。清者为天浊为地。涎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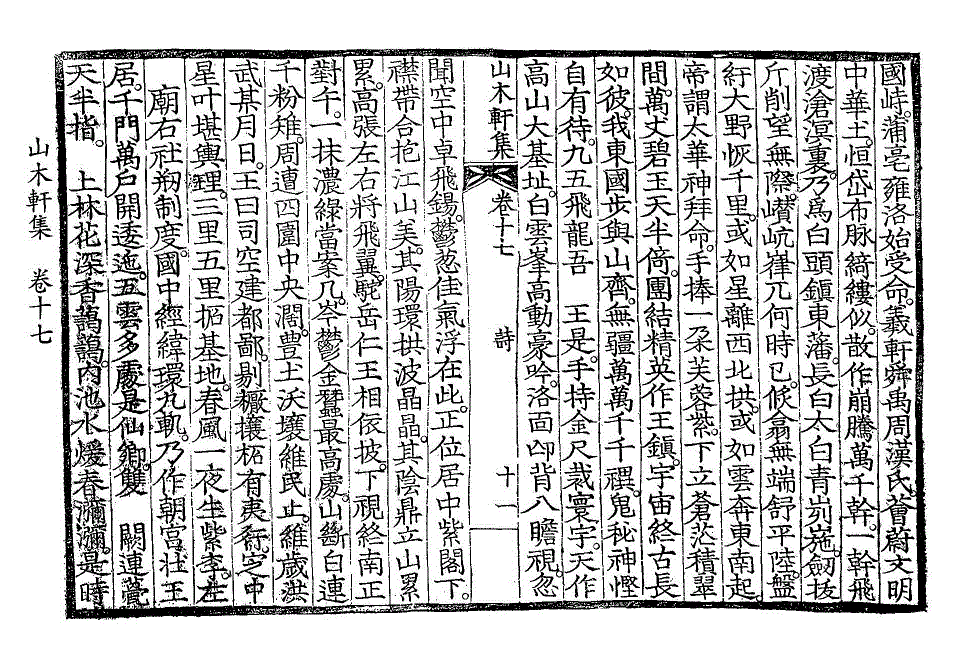 国峙。蒲亳雍洛始受命。羲轩舜禹周汉氏。荟蔚文明中华土。恒岱布脉绮缕似。散作崩腾万千干。一干飞渡沧溟里。乃为白头镇东藩。长白太白青峛崺。剑拔斤削望无际。巑岏嵂兀何时已。倏翕无端舒平陆。盘纡大野恢千里。或如星离西北拱。或如云奔东南起。帝谓太华神拜命。手捧一朵芙蓉紫。下立苍茫积翠间。万丈碧玉天半倚。团结精英作王镇。宇宙终古长如彼。我东国步与山齐。无疆万万千千祀。鬼秘神悭自有待。九五飞龙吾 王是。手持金尺裁寰宇。天作高山大基址。白云峰高动豪吟。洛面邙背八瞻视。忽闻空中卓飞锡。郁葱佳气浮在此。正位居中紫阁下。襟带合抱江山美。其阳环拱波晶晶。其阴鼎立山累累。高张左右将飞翼。驼岳仁王相依披。下视终南正对午。一抹浓绿当案几。岑郁金蚕最高处。山断白连千粉雉。周遭四围中央阔。礼土沃壤维民止。维岁洪武某月日。王曰司空建都鄙。剔𣝓攘柘有夷行。定中星叶堪舆理。三里五里拓基地。春风一夜生紫李。左 庙右社刱制度。国中经纬环九轨。乃作朝宫壮王居。千门万户开逶迤。五云多处是仙乡。双 阙连甍天半指。 上林花深香蔼蔼。内池水煖春瀰瀰。是时
国峙。蒲亳雍洛始受命。羲轩舜禹周汉氏。荟蔚文明中华土。恒岱布脉绮缕似。散作崩腾万千干。一干飞渡沧溟里。乃为白头镇东藩。长白太白青峛崺。剑拔斤削望无际。巑岏嵂兀何时已。倏翕无端舒平陆。盘纡大野恢千里。或如星离西北拱。或如云奔东南起。帝谓太华神拜命。手捧一朵芙蓉紫。下立苍茫积翠间。万丈碧玉天半倚。团结精英作王镇。宇宙终古长如彼。我东国步与山齐。无疆万万千千祀。鬼秘神悭自有待。九五飞龙吾 王是。手持金尺裁寰宇。天作高山大基址。白云峰高动豪吟。洛面邙背八瞻视。忽闻空中卓飞锡。郁葱佳气浮在此。正位居中紫阁下。襟带合抱江山美。其阳环拱波晶晶。其阴鼎立山累累。高张左右将飞翼。驼岳仁王相依披。下视终南正对午。一抹浓绿当案几。岑郁金蚕最高处。山断白连千粉雉。周遭四围中央阔。礼土沃壤维民止。维岁洪武某月日。王曰司空建都鄙。剔𣝓攘柘有夷行。定中星叶堪舆理。三里五里拓基地。春风一夜生紫李。左 庙右社刱制度。国中经纬环九轨。乃作朝宫壮王居。千门万户开逶迤。五云多处是仙乡。双 阙连甍天半指。 上林花深香蔼蔼。内池水煖春瀰瀰。是时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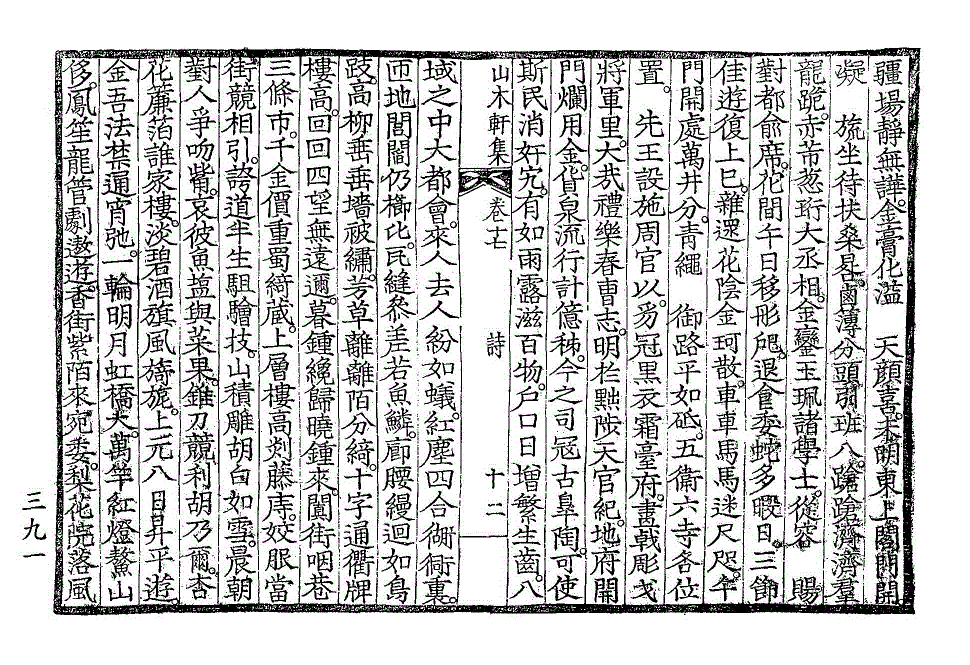 疆场静无哗。金膏化溢 天颜喜。未明东上阁门开。凝 旒坐待扶桑晷。卤簿分头引班入。跄跄济济群龙跪。赤芾葱珩大丞相。金銮玉佩诸学士。从容 赐对都俞席。花间午日移彤戺。退食委蛇多暇日。三节佳游复上已。杂遝花阴金珂散。车车马马迷尺咫。午门开处万井分。青绳 御路平如砥。五卫六寺各位置。 先王设施周官以。豸冠黑衣霜台府。画戟彫戈将军里。大哉礼乐春曹志。明于黜陟天官纪。地府开门烂用金。货泉流行计亿秭。今之司寇古皋陶。可使斯民消奸宄。有如雨露滋百物。户口日增繁生齿。八域之中大都会。来人去人纷如蚁。红尘四合胡衕里。匝地闾阎仍栉比。瓦缝参差若鱼鳞。廊腰缦回如鸟跂。高柳垂垂墙被绣。芳草离离陌分绮。十字通衢牌楼高。回回四望无远迩。暮钟才归晓钟来。阗街咽巷三条市。千金价重蜀绮藏。上层楼高剡藤庤。姣服当街竞相引。誇道半生驵𩦱技。山积雕胡白如雪。晨朝对人争吻觜。哀彼鱼盐与菜果。锥刀竞利胡乃尔。杏花帘箔谁家楼。淡碧酒旗风旖旎。上元八日升平游。金吾法禁通宵弛。一轮明月虹桥大。万竿红灯鳌山侈。凤笙龙管剧遨游。香街紫陌来宛委。梨花院落风
疆场静无哗。金膏化溢 天颜喜。未明东上阁门开。凝 旒坐待扶桑晷。卤簿分头引班入。跄跄济济群龙跪。赤芾葱珩大丞相。金銮玉佩诸学士。从容 赐对都俞席。花间午日移彤戺。退食委蛇多暇日。三节佳游复上已。杂遝花阴金珂散。车车马马迷尺咫。午门开处万井分。青绳 御路平如砥。五卫六寺各位置。 先王设施周官以。豸冠黑衣霜台府。画戟彫戈将军里。大哉礼乐春曹志。明于黜陟天官纪。地府开门烂用金。货泉流行计亿秭。今之司寇古皋陶。可使斯民消奸宄。有如雨露滋百物。户口日增繁生齿。八域之中大都会。来人去人纷如蚁。红尘四合胡衕里。匝地闾阎仍栉比。瓦缝参差若鱼鳞。廊腰缦回如鸟跂。高柳垂垂墙被绣。芳草离离陌分绮。十字通衢牌楼高。回回四望无远迩。暮钟才归晓钟来。阗街咽巷三条市。千金价重蜀绮藏。上层楼高剡藤庤。姣服当街竞相引。誇道半生驵𩦱技。山积雕胡白如雪。晨朝对人争吻觜。哀彼鱼盐与菜果。锥刀竞利胡乃尔。杏花帘箔谁家楼。淡碧酒旗风旖旎。上元八日升平游。金吾法禁通宵弛。一轮明月虹桥大。万竿红灯鳌山侈。凤笙龙管剧遨游。香街紫陌来宛委。梨花院落风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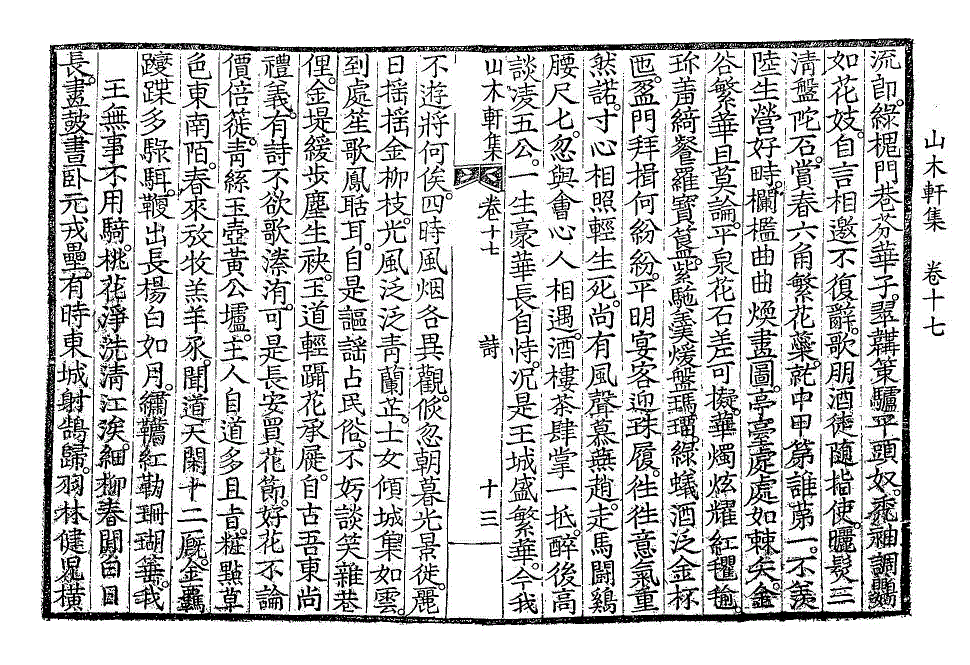 流即。绿槐门巷芬华子。翠韝策驴平头奴。秃袖调鹦如花妓。自言相邀不复辞。歌朋酒徒随指使。晒发三清盘陀石。赏春六角繁花蕊。就中甲第谁第一。不羡陆生营好畤。栏槛曲曲焕画图。亭台处处如棘矢。金谷繁华且莫论。平泉花石差可拟。华烛炫耀红𣰽毹。珍羞绮餐罗宝簋。紫驼羹煖盘玛琉。绿蚁酒泛金杯匜。盈门拜揖何纷纷。平明宴客迎珠履。往往意气重然诺。寸心相照轻生死。尚有风声慕燕赵。走马斗鸡腰尺匕。忽与会心人相遇。酒楼茶肆掌一抵。醉后高谈凌五公。一生豪华长自恃。况是王城盛繁华。今我不游将何俟。四时风烟各异观。倏忽朝暮光景徙。丽日摇摇金柳枝。光风泛泛青兰芷。士女倾城集如云。到处笙歌凤聒耳。自是讴谣占民俗。不妨谈笑杂巷俚。金堤缓步尘生袂。玉道轻蹑花承屣。自古吾东尚礼义。有诗不欲歌溱洧。可是长安买花节。好花不论价倍蓰。青丝玉壶黄公垆。主人自道多且旨。妆点草色东南陌。春来放牧羔羊豕。闻道天闲十二厩。金羁躞蹀多騄駬。鞭出长杨白如月。绣鞯红勒珊瑚箠。我 王无事不用骑。桃花净洗清江涘。细柳春閒白日长。画鼓昼卧元戎垒。有时东城射鹄归。羽林健儿横
流即。绿槐门巷芬华子。翠韝策驴平头奴。秃袖调鹦如花妓。自言相邀不复辞。歌朋酒徒随指使。晒发三清盘陀石。赏春六角繁花蕊。就中甲第谁第一。不羡陆生营好畤。栏槛曲曲焕画图。亭台处处如棘矢。金谷繁华且莫论。平泉花石差可拟。华烛炫耀红𣰽毹。珍羞绮餐罗宝簋。紫驼羹煖盘玛琉。绿蚁酒泛金杯匜。盈门拜揖何纷纷。平明宴客迎珠履。往往意气重然诺。寸心相照轻生死。尚有风声慕燕赵。走马斗鸡腰尺匕。忽与会心人相遇。酒楼茶肆掌一抵。醉后高谈凌五公。一生豪华长自恃。况是王城盛繁华。今我不游将何俟。四时风烟各异观。倏忽朝暮光景徙。丽日摇摇金柳枝。光风泛泛青兰芷。士女倾城集如云。到处笙歌凤聒耳。自是讴谣占民俗。不妨谈笑杂巷俚。金堤缓步尘生袂。玉道轻蹑花承屣。自古吾东尚礼义。有诗不欲歌溱洧。可是长安买花节。好花不论价倍蓰。青丝玉壶黄公垆。主人自道多且旨。妆点草色东南陌。春来放牧羔羊豕。闻道天闲十二厩。金羁躞蹀多騄駬。鞭出长杨白如月。绣鞯红勒珊瑚箠。我 王无事不用骑。桃花净洗清江涘。细柳春閒白日长。画鼓昼卧元戎垒。有时东城射鹄归。羽林健儿横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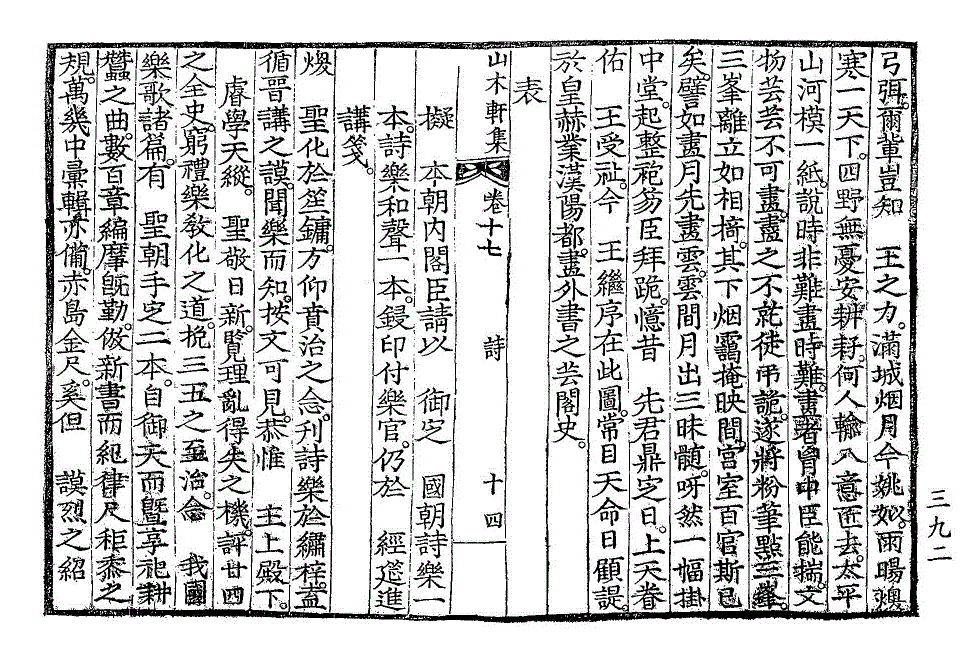 弓弭。尔辈岂知 王之力。满城烟月今姚姒。雨旸燠寒一天下。四野无忧安耕耔。何人输入意匠去。太平山河模一纸。说时非难画时难。画者胸中臣能揣。文物芸芸不可画。画之不就徒吊诡。遂将粉笔点三峰。三峰离立如相掎。其下烟霭掩映间。宫室百官斯已矣。譬如画月先画云。云间月出三昧髓。呀然一幅挂中堂。起整袍笏臣拜跪。忆昔 先君鼎定日。上天眷佑 王受祉。今 王继序在此图。常目天命日顾諟。于皇赫业汉阳都。画外书之芸阁史。
弓弭。尔辈岂知 王之力。满城烟月今姚姒。雨旸燠寒一天下。四野无忧安耕耔。何人输入意匠去。太平山河模一纸。说时非难画时难。画者胸中臣能揣。文物芸芸不可画。画之不就徒吊诡。遂将粉笔点三峰。三峰离立如相掎。其下烟霭掩映间。宫室百官斯已矣。譬如画月先画云。云间月出三昧髓。呀然一幅挂中堂。起整袍笏臣拜跪。忆昔 先君鼎定日。上天眷佑 王受祉。今 王继序在此图。常目天命日顾諟。于皇赫业汉阳都。画外书之芸阁史。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表
拟 本朝内阁臣请以 御定 国朝诗乐一本。诗乐和声一本。锓印付乐官。仍于 经筵进讲笺。
焕 圣化于笙镛。方仰贲治之念。刊诗乐于绣梓。盍循晋讲之谟。闻乐而知。按文可见。恭惟 主上殿下。 睿学天纵。 圣敬日新。览理乱得失之机。评廿四之全史。穷礼乐教化之道。挽三五之至治。念 我国乐歌诸篇。有 圣朝手定二本。自御天而暨享祀耕蚕之曲。数百章编摩既勤。仿新书而纪律尺秬黍之规。万几中汇辑亦备。赤岛金尺。奚但 谟烈之绍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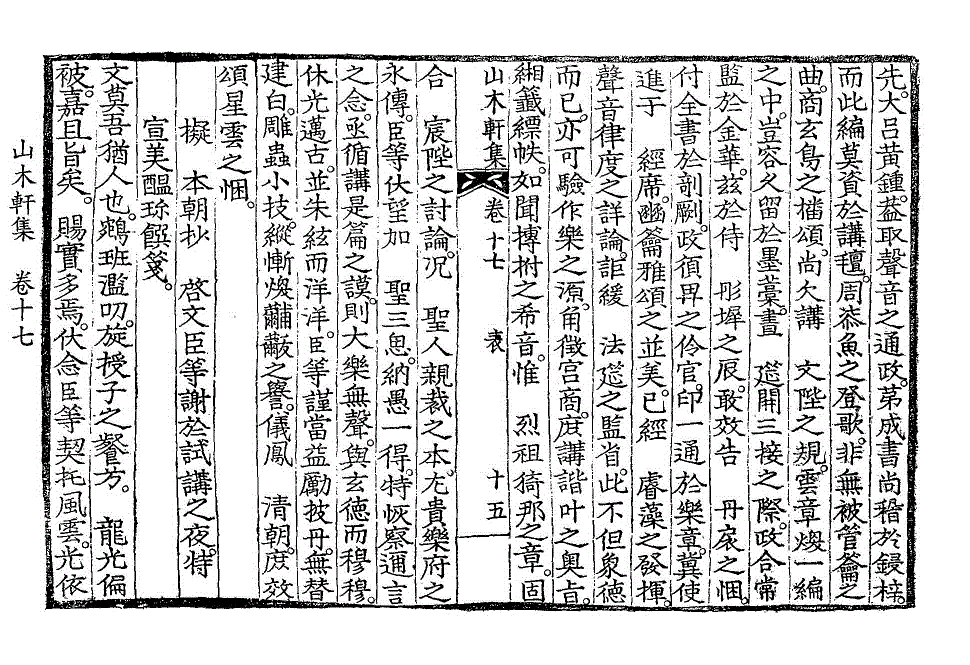 先。大吕黄钟。盖取声音之通政。第成书尚稽于锓梓。而此编莫资于讲毡。周㓒鱼之登歌。非无被管籥之曲。商玄鸟之播颂。尚欠讲 文陛之规。云章焕一编之中。岂容久留于墨藁。昼 筵开三接之际。政合常监于金华。玆于侍 彤墀之辰。敢效告 丹扆之悃。付全书于剞劂。政须畀之伶官。印一通于乐章。冀使进于 经席。豳籥雅颂之并美。已经 睿藻之发挥。声音律度之详论。讵缓 法筵之监省。此不但象德而已。亦可验作乐之源。角徵宫商。庶讲谐叶之奥旨。缃签缥帙。如闻搏拊之希音。惟 烈祖猗那之章。固合 宸陛之讨论。况 圣人亲裁之本。尤贵乐府之永传。臣等伏望加 圣三思。纳愚一得。特恢察迩言之念。亟循讲是篇之谟。则大乐无声。与玄德而穆穆。休光迈古。并朱弦而洋洋。臣等谨当益励披丹。无替建白。雕虫小技。纵惭焕黼黻之誉。仪凤 清朝。庶效颂星云之悃。
先。大吕黄钟。盖取声音之通政。第成书尚稽于锓梓。而此编莫资于讲毡。周㓒鱼之登歌。非无被管籥之曲。商玄鸟之播颂。尚欠讲 文陛之规。云章焕一编之中。岂容久留于墨藁。昼 筵开三接之际。政合常监于金华。玆于侍 彤墀之辰。敢效告 丹扆之悃。付全书于剞劂。政须畀之伶官。印一通于乐章。冀使进于 经席。豳籥雅颂之并美。已经 睿藻之发挥。声音律度之详论。讵缓 法筵之监省。此不但象德而已。亦可验作乐之源。角徵宫商。庶讲谐叶之奥旨。缃签缥帙。如闻搏拊之希音。惟 烈祖猗那之章。固合 宸陛之讨论。况 圣人亲裁之本。尤贵乐府之永传。臣等伏望加 圣三思。纳愚一得。特恢察迩言之念。亟循讲是篇之谟。则大乐无声。与玄德而穆穆。休光迈古。并朱弦而洋洋。臣等谨当益励披丹。无替建白。雕虫小技。纵惭焕黼黻之誉。仪凤 清朝。庶效颂星云之悃。拟 本朝抄 启文臣等谢于试讲之夜。特 宣美酝珍馔笺。
文莫吾犹人也。鹓班滥叨。旋授子之餐方。 龙光偏被。嘉且旨矣。 赐实多焉。伏念臣等契托风云。光依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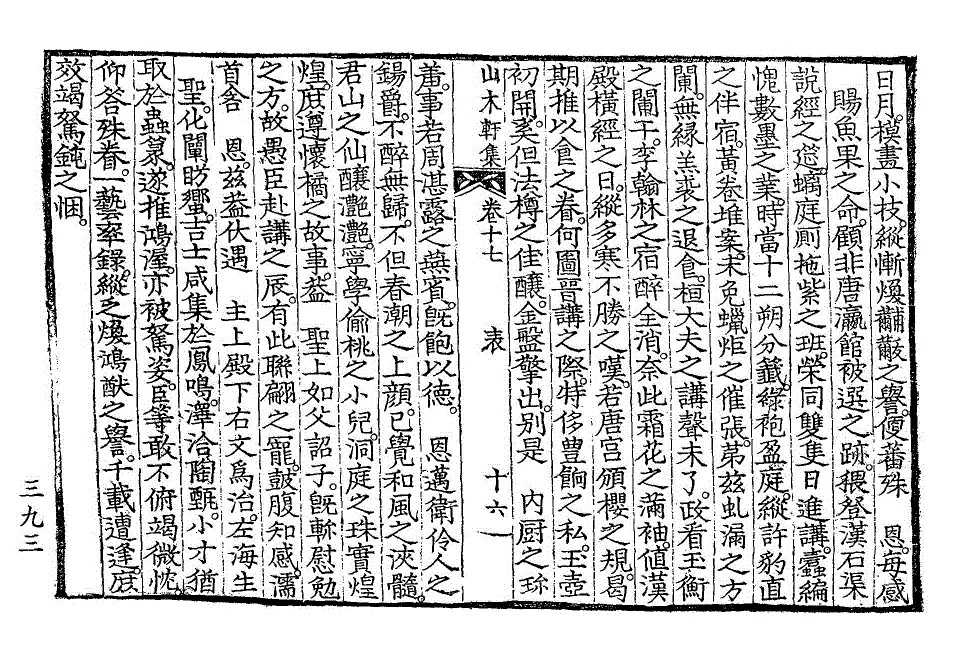 日月。模画小技。纵惭焕黼黻之誉。便蕃殊 恩。每感 赐鱼果之命。顾非唐瀛馆被选之迹。猥登汉石渠说经之筵。螭庭厕拖紫之班。荣同双只日进讲。蠹编愧数墨之业。时当十二朔分签。绿袍盈庭。纵许豹直之伴宿。黄卷堆案。未免蜡炬之催张。第玆虬漏之方阑。无缘羔裘之退食。桓大夫之讲声未了。政看玉衡之阑干。李翰林之宿醉全消。奈此霜花之满袖。值汉殿横经之日。纵多寒不胜之叹。若唐宫颁樱之规。曷期推以食之眷。何图晋讲之际。特侈礼饷之私。玉壶初开。奚但法樽之佳酿。金盘擎出。别是 内厨之珍羞。事若周湛露之燕宾。既饱以德。 恩迈卫伶人之锡爵。不醉无归。不但春潮之上颜。已觉和风之浃髓。君山之仙酿滟滟。宁学偷桃之小儿。洞庭之珠实煌煌。庶遵怀橘之故事。盖 圣上如父诏子。既轸慰勉之方。故愚臣赴讲之辰。有此联翩之宠。鼓腹知感。濡首含 恩。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右文为治。左海生 圣。化阐盻蚃。吉士咸集于凤鸣。泽洽陶甄。小才犹取于虫篆。遂推鸿渥。亦被驽姿。臣等敢不俯竭微忱。仰答殊眷。一艺率录。纵乏焕鸿猷之誉。千载遭逢。庶效竭驽钝之悃。
日月。模画小技。纵惭焕黼黻之誉。便蕃殊 恩。每感 赐鱼果之命。顾非唐瀛馆被选之迹。猥登汉石渠说经之筵。螭庭厕拖紫之班。荣同双只日进讲。蠹编愧数墨之业。时当十二朔分签。绿袍盈庭。纵许豹直之伴宿。黄卷堆案。未免蜡炬之催张。第玆虬漏之方阑。无缘羔裘之退食。桓大夫之讲声未了。政看玉衡之阑干。李翰林之宿醉全消。奈此霜花之满袖。值汉殿横经之日。纵多寒不胜之叹。若唐宫颁樱之规。曷期推以食之眷。何图晋讲之际。特侈礼饷之私。玉壶初开。奚但法樽之佳酿。金盘擎出。别是 内厨之珍羞。事若周湛露之燕宾。既饱以德。 恩迈卫伶人之锡爵。不醉无归。不但春潮之上颜。已觉和风之浃髓。君山之仙酿滟滟。宁学偷桃之小儿。洞庭之珠实煌煌。庶遵怀橘之故事。盖 圣上如父诏子。既轸慰勉之方。故愚臣赴讲之辰。有此联翩之宠。鼓腹知感。濡首含 恩。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右文为治。左海生 圣。化阐盻蚃。吉士咸集于凤鸣。泽洽陶甄。小才犹取于虫篆。遂推鸿渥。亦被驽姿。臣等敢不俯竭微忱。仰答殊眷。一艺率录。纵乏焕鸿猷之誉。千载遭逢。庶效竭驽钝之悃。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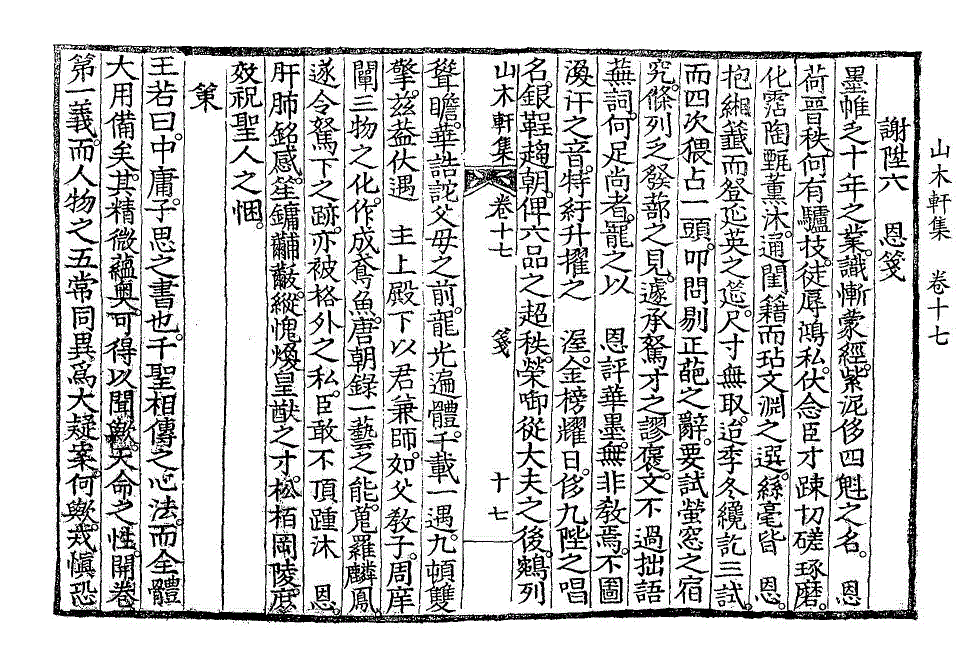 谢升六 恩笺
谢升六 恩笺墨帷乏十年之业。识惭蒙经。紫泥侈四魁之名。 恩荷晋秩。何有驴技。徒辱鸿私。伏念臣才疏切磋琢磨。化沾陶甄薰沐。通闺籍而玷文渊之选。丝毫皆 恩。抱缃签而登延英之筵。尺寸无取。迨季冬才讫三试。而四次猥占一头。叩问剔正葩之辞。要试萤窗之宿究。条列乏发蔀之见。遽承驽才之谬褒。文不过拙语芜词。何足尚者。宠之以 恩评华墨。无非教焉。不图涣汗之音。特纡升擢之 渥。金榜耀日。侈九陛之唱名。银鞓趋朝。俾六品之超秩。荣衔从大夫之后。鹓列耸瞻。华诰詑父母之前。龙光遍体。千载一遇。九顿双擎。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以君兼师。如父教子。周庠阐三物之化。作成鸢鱼。唐朝录一艺之能。蒐罗麟凤遂令驽下之迹。亦被格外之私。臣敢不顶踵沐 恩。肝肺铭感。笙镛黼黻。纵愧焕皇猷之才。松柏冈陵。庶效祝圣人之悃。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策
[中庸书]
王若曰。中庸。子思之书也。千圣相传之心法。而全体大用备矣。其精微蕴奥。可得以闻欤。天命之性。开卷第一义。而人物之五常同异为大疑案。何欤。戒慎恐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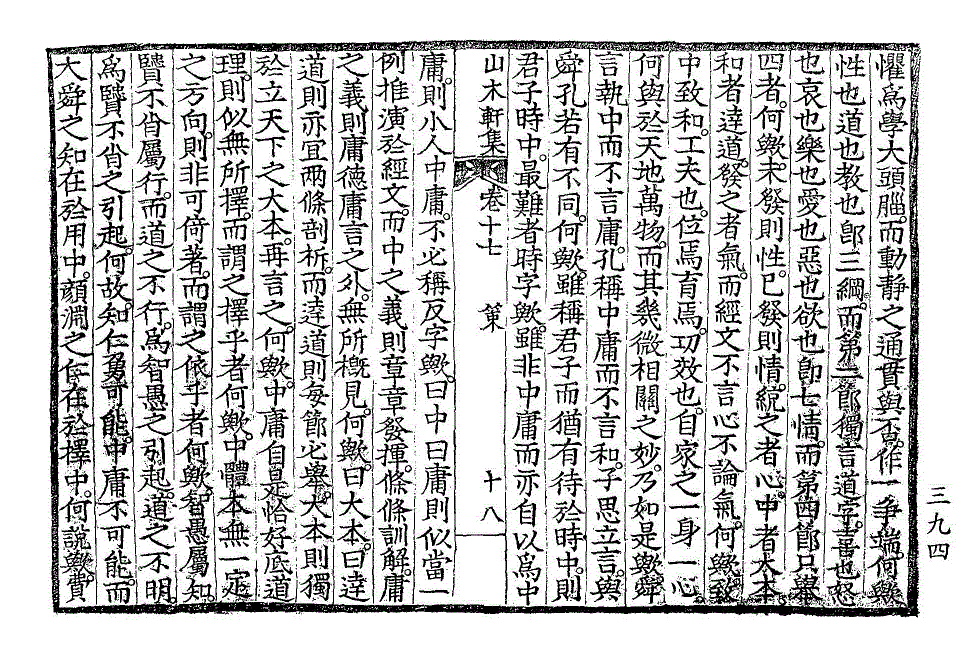 惧为学大头脑。而动静之通贯与否。作一争端。何欤。性也道也教也即三纲。而第二节独言道字。喜也怒也哀也乐也爱也恶也欲也即七情。而第四节只举四者。何欤。未发则性。已发则情。统之者心。中者大本。和者达道。发之者气。而经文不言心不论气。何欤。致中致和。工夫也。位焉育焉。功效也。自家之一身一心。何与于天地万物。而其几微相关之妙。乃如是欤。舜言执中而不言庸。孔称中庸而不言和。子思立言。与舜孔若有不同。何欤。虽称君子而犹有待于时中。则君子时中。最难者时字欤。虽非中庸而亦自以为中庸。则小人中庸。不必称反字欤。曰中曰庸则似当一例推演于经文。而中之义则章章发挥。条条训解。庸之义则庸德庸言之外。无所概见。何欤。曰大本。曰达道则亦宜两条剖析。而达道则每节必举。大本则独于立天下之大本。再言之。何欤。中庸自是恰好底道理。则似无所择。而谓之择乎者何欤。中体本无一定之方向。则非可倚著。而谓之依乎者何欤。智愚属知。贤不肖属行。而道之不行。为智愚之引起。道之不明。为贤不肖之引起。何故。知仁勇可能。中庸不可能。而大舜之知在于用中。颜渊之仁在于择中。何说欤。费
惧为学大头脑。而动静之通贯与否。作一争端。何欤。性也道也教也即三纲。而第二节独言道字。喜也怒也哀也乐也爱也恶也欲也即七情。而第四节只举四者。何欤。未发则性。已发则情。统之者心。中者大本。和者达道。发之者气。而经文不言心不论气。何欤。致中致和。工夫也。位焉育焉。功效也。自家之一身一心。何与于天地万物。而其几微相关之妙。乃如是欤。舜言执中而不言庸。孔称中庸而不言和。子思立言。与舜孔若有不同。何欤。虽称君子而犹有待于时中。则君子时中。最难者时字欤。虽非中庸而亦自以为中庸。则小人中庸。不必称反字欤。曰中曰庸则似当一例推演于经文。而中之义则章章发挥。条条训解。庸之义则庸德庸言之外。无所概见。何欤。曰大本。曰达道则亦宜两条剖析。而达道则每节必举。大本则独于立天下之大本。再言之。何欤。中庸自是恰好底道理。则似无所择。而谓之择乎者何欤。中体本无一定之方向。则非可倚著。而谓之依乎者何欤。智愚属知。贤不肖属行。而道之不行。为智愚之引起。道之不明。为贤不肖之引起。何故。知仁勇可能。中庸不可能。而大舜之知在于用中。颜渊之仁在于择中。何说欤。费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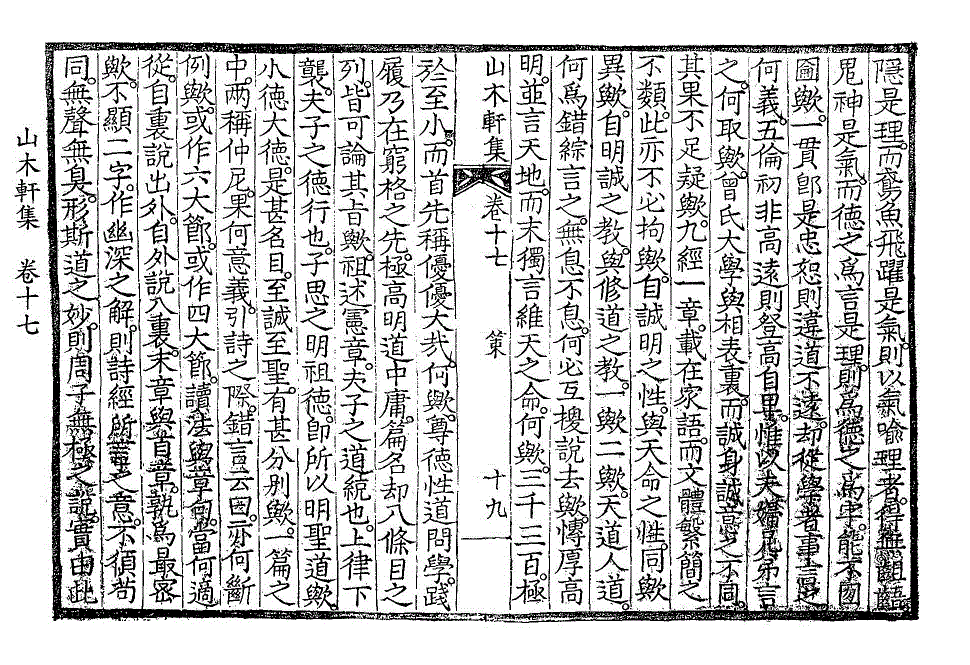 隐是理。而鸢鱼飞跃是气。则以气喻理者。得无龃龉。鬼神是气。而德之为言是理。则为德之为字。能不囫囵欤。一贯即是忠恕则违道不远。却从学者事言之。何义。五伦初非高远则登高自卑。惟以夫妇兄弟言之。何取欤。曾氏大学与相表里。而诚身诚意之不同。其果不足疑欤。九经一章。载在家语。而文体繁简之不类。此亦不必拘欤。自诚明之性。与天命之性。同欤异欤。自明诚之教。与修道之教。一欤二欤。天道人道。何为错综言之。无息不息。何必互换说去欤。博厚高明。并言天地。而末独言维天之命。何欤。三千三百。极于至小。而首先称优优大哉。何欤。尊德性道问学。践履乃在穷格之先。极高明道中庸。篇名却八条目之列。皆可论其旨欤。祖述宪章。夫子之道统也。上律下袭。夫子之德行也。子思之明祖德。即所以明圣道欤。小德大德。是甚名目。至诚至圣。有甚分别欤。一篇之中。两称仲尼。果何意义。引诗之际。错言云曰。亦何断例欤。或作六大节。或作四大节。读法与章句。当何适从。自里说出外。自外说入里。末章与首章。孰为最密欤。不显二字。作幽深之解。则诗经所言之意。不须苟同。无声无臭。形斯道之妙。则周子无极之说。实由此
隐是理。而鸢鱼飞跃是气。则以气喻理者。得无龃龉。鬼神是气。而德之为言是理。则为德之为字。能不囫囵欤。一贯即是忠恕则违道不远。却从学者事言之。何义。五伦初非高远则登高自卑。惟以夫妇兄弟言之。何取欤。曾氏大学与相表里。而诚身诚意之不同。其果不足疑欤。九经一章。载在家语。而文体繁简之不类。此亦不必拘欤。自诚明之性。与天命之性。同欤异欤。自明诚之教。与修道之教。一欤二欤。天道人道。何为错综言之。无息不息。何必互换说去欤。博厚高明。并言天地。而末独言维天之命。何欤。三千三百。极于至小。而首先称优优大哉。何欤。尊德性道问学。践履乃在穷格之先。极高明道中庸。篇名却八条目之列。皆可论其旨欤。祖述宪章。夫子之道统也。上律下袭。夫子之德行也。子思之明祖德。即所以明圣道欤。小德大德。是甚名目。至诚至圣。有甚分别欤。一篇之中。两称仲尼。果何意义。引诗之际。错言云曰。亦何断例欤。或作六大节。或作四大节。读法与章句。当何适从。自里说出外。自外说入里。末章与首章。孰为最密欤。不显二字。作幽深之解。则诗经所言之意。不须苟同。无声无臭。形斯道之妙。则周子无极之说。实由此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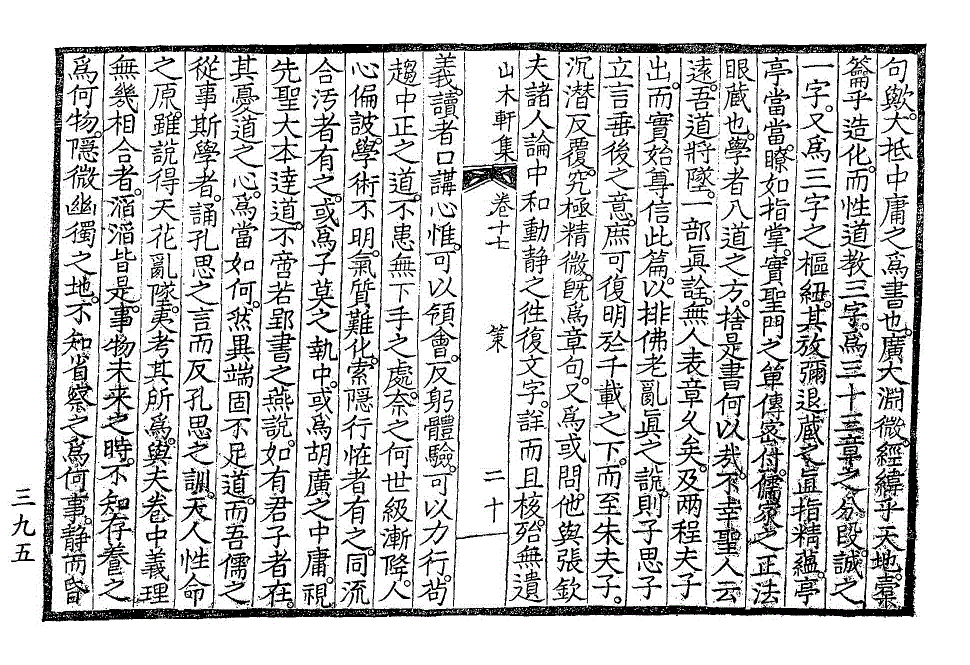 句欤。大抵中庸之为书也。广大渊微。经纬乎天地。橐籥乎造化。而性道教三字。为三十三章之分段。诚之一字。又为三字之枢纽。其放弥退藏之直指精蕴。亭亭当当。瞭如指掌。实圣门之单传密付。儒家之正法眼藏也。学者八道之方。舍是书何以哉。不幸圣人云远。吾道将坠。一部真诠。无人表章久矣。及两程夫子出。而实始尊信此篇。以排佛老乱真之说。则子思子立言垂后之意。庶可复明于千载之下。而至朱夫子。沉潜反覆。究极精微。既为章句。又为或问。他与张钦夫诸人论中和动静之往复文字。详而且核。殆无遗义。读者口讲心惟。可以领会。反躬体验。可以力行。苟趋中正之道。不患无下手之处。奈之何世级渐降。人心偏诐。学术不明。气质难化。索隐行怪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或为子莫之执中。或为胡广之中庸。视先圣大本达道。不啻若郢书之燕说。如有君子者在。其忧道之心。为当如何。然异端固不足道。而吾儒之从事斯学者。诵孔思之言而反孔思之训。天人性命之原。虽说得天花乱坠。夷考其所为。与夫卷中义理无几相合者。滔滔皆是。事物未来之时。不知存养之为何物。隐微幽独之地。不知省察之为何事。静而昏
句欤。大抵中庸之为书也。广大渊微。经纬乎天地。橐籥乎造化。而性道教三字。为三十三章之分段。诚之一字。又为三字之枢纽。其放弥退藏之直指精蕴。亭亭当当。瞭如指掌。实圣门之单传密付。儒家之正法眼藏也。学者八道之方。舍是书何以哉。不幸圣人云远。吾道将坠。一部真诠。无人表章久矣。及两程夫子出。而实始尊信此篇。以排佛老乱真之说。则子思子立言垂后之意。庶可复明于千载之下。而至朱夫子。沉潜反覆。究极精微。既为章句。又为或问。他与张钦夫诸人论中和动静之往复文字。详而且核。殆无遗义。读者口讲心惟。可以领会。反躬体验。可以力行。苟趋中正之道。不患无下手之处。奈之何世级渐降。人心偏诐。学术不明。气质难化。索隐行怪者有之。同流合污者有之。或为子莫之执中。或为胡广之中庸。视先圣大本达道。不啻若郢书之燕说。如有君子者在。其忧道之心。为当如何。然异端固不足道。而吾儒之从事斯学者。诵孔思之言而反孔思之训。天人性命之原。虽说得天花乱坠。夷考其所为。与夫卷中义理无几相合者。滔滔皆是。事物未来之时。不知存养之为何物。隐微幽独之地。不知省察之为何事。静而昏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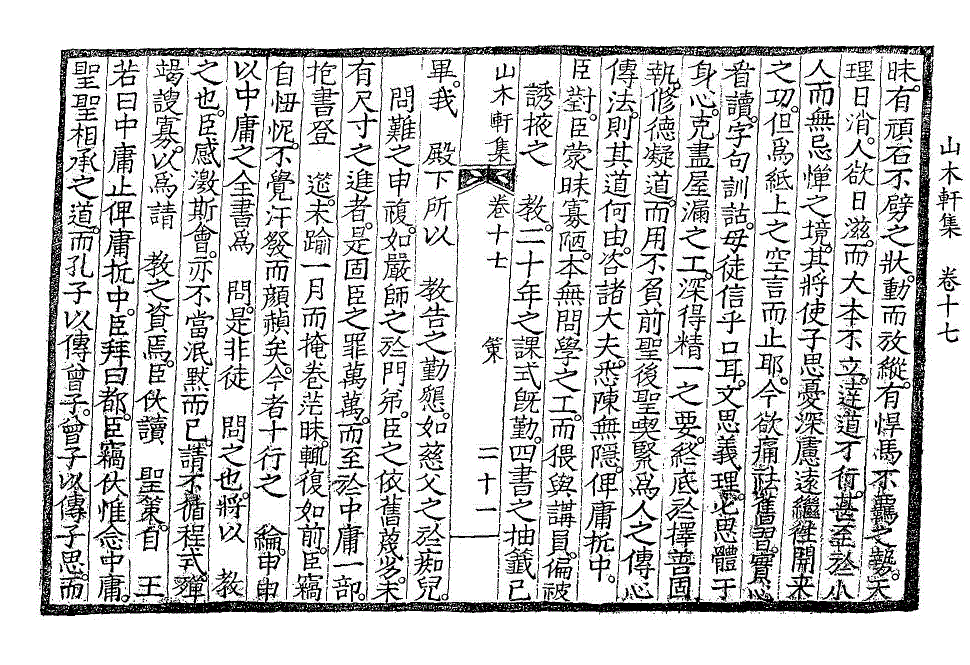 昧。有顽石不劈之状。动而放纵。有悍马不羁之势。天理日消。人欲日滋。而大本不立。达道不行。甚至于小人而无忌惮之境。其将使子思忧深虑远继往开来之功。但为纸上之空言而止耶。今欲痛祛旧习。实心看读。字句训诂。毋徒信乎口耳。文思义理。必思体于身心。克尽屋漏之工。深得精一之要。终底于择善固执。修德凝道。而用不负前圣后圣吃紧为人之传心传法。则其道何由。咨诸大夫。悉陈无隐。俾庸折中。
昧。有顽石不劈之状。动而放纵。有悍马不羁之势。天理日消。人欲日滋。而大本不立。达道不行。甚至于小人而无忌惮之境。其将使子思忧深虑远继往开来之功。但为纸上之空言而止耶。今欲痛祛旧习。实心看读。字句训诂。毋徒信乎口耳。文思义理。必思体于身心。克尽屋漏之工。深得精一之要。终底于择善固执。修德凝道。而用不负前圣后圣吃紧为人之传心传法。则其道何由。咨诸大夫。悉陈无隐。俾庸折中。臣对。臣蒙昧寡陋。本无问学之工。而猥与讲员。偏被 诱掖之 教。二十年之课式既勤。四书之抽签已毕。我 殿下所以 教告之勤恳。如慈父之于痴儿。 问难之申复。如严师之于门弟。臣之依旧蔑劣。未有尺寸之进者。是固臣之罪万万。而至于中庸一部。抱书登 筵。未踰一月而掩卷茫昧。辄复如前。臣窃自忸怩。不觉汗发而颜赪矣。今者十行之 纶。申申以中庸之全书为 问。是非徒 问之也。将以 教之也。臣感激斯会。亦不当泯默而已。请不循程式。殚竭謏寡。以为请 教之资焉。臣伏读 圣策。自 王若曰中庸止俾庸折中。臣拜曰都。臣窃伏惟念中庸。圣圣相承之道。而孔子以传曾子。曾子以传子思。而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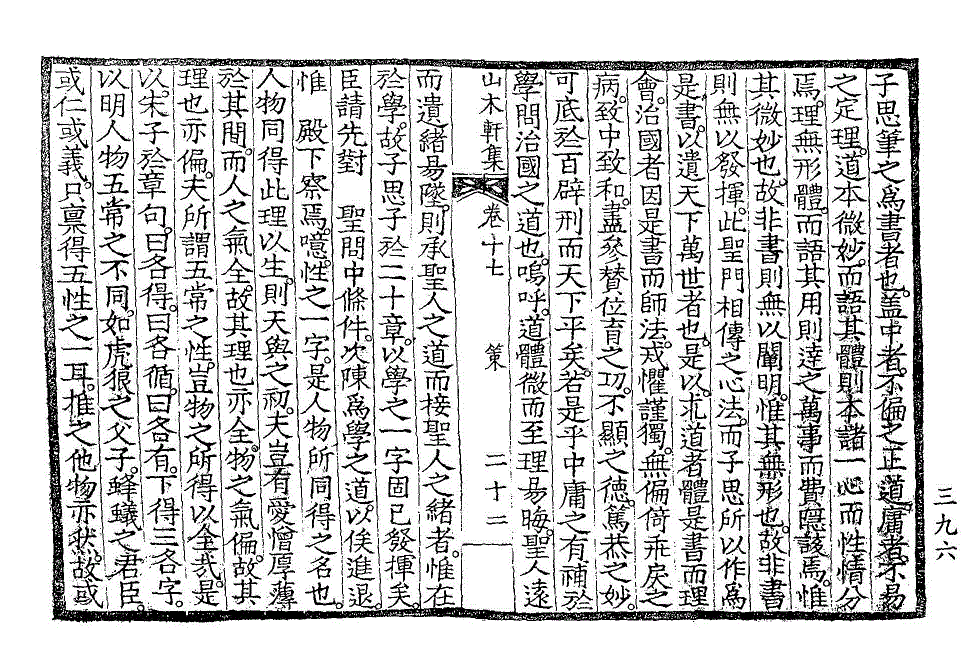 子思笔之为书者也。盖中者。不偏之正道。庸者。不易之定理。道本微妙。而语其体则本诸一心而性情分焉。理无形体。而语其用则达之万事而费隐该焉。惟其微妙也。故非书则无以阐明。惟其无形也。故非书则无以发挥。此圣门相传之心法。而子思所以作为是书。以遗天下万世者也。是以。求道者体是书而理会。治国者因是书而师法。戒惧谨独。无偏倚乖戾之病。致中致和。尽参赞位育之功。不显之德。笃恭之妙。可底于百辟刑而天下平矣。若是乎中庸之有补于学问治国之道也。呜呼。道体微而至理易晦。圣人远而遗绪易坠。则承圣人之道而接圣人之绪者。惟在于学。故子思子于二十章。以学之一字固已发挥矣。臣请先对 圣问中条件。次陈为学之道。以俟进退。惟 殿下察焉。噫。性之一字。是人物所同得之名也。人物同得此理以生。则天与之初。夫岂有爱憎厚薄于其间。而人之气全。故其理也亦全。物之气偏。故其理也亦偏。夫所谓五常之性。岂物之所得以全哉。是以。朱子于章句。曰各得。曰各循。曰各有。下得三各字。以明人物五常之不同。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或仁或义。只禀得五性之一耳。推之他物亦然。故或
子思笔之为书者也。盖中者。不偏之正道。庸者。不易之定理。道本微妙。而语其体则本诸一心而性情分焉。理无形体。而语其用则达之万事而费隐该焉。惟其微妙也。故非书则无以阐明。惟其无形也。故非书则无以发挥。此圣门相传之心法。而子思所以作为是书。以遗天下万世者也。是以。求道者体是书而理会。治国者因是书而师法。戒惧谨独。无偏倚乖戾之病。致中致和。尽参赞位育之功。不显之德。笃恭之妙。可底于百辟刑而天下平矣。若是乎中庸之有补于学问治国之道也。呜呼。道体微而至理易晦。圣人远而遗绪易坠。则承圣人之道而接圣人之绪者。惟在于学。故子思子于二十章。以学之一字固已发挥矣。臣请先对 圣问中条件。次陈为学之道。以俟进退。惟 殿下察焉。噫。性之一字。是人物所同得之名也。人物同得此理以生。则天与之初。夫岂有爱憎厚薄于其间。而人之气全。故其理也亦全。物之气偏。故其理也亦偏。夫所谓五常之性。岂物之所得以全哉。是以。朱子于章句。曰各得。曰各循。曰各有。下得三各字。以明人物五常之不同。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或仁或义。只禀得五性之一耳。推之他物亦然。故或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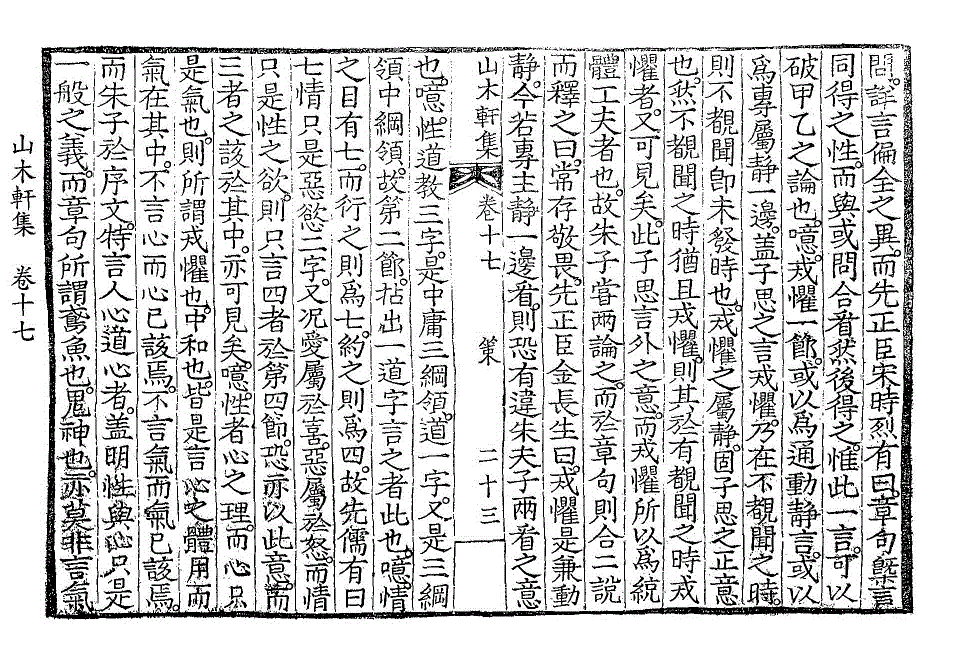 问。详言偏全之异。而先正臣宋时烈有曰。章句槩言同得之性。而与或问合看然后得之。惟此一言。可以破甲乙之论也。噫。戒惧一节。或以为通动静言。或以为专属静一边。盖子思之言戒惧。乃在不睹闻之时。则不睹闻即未发时也。戒惧之属静。固子思之正意也。然不睹闻之时犹且戒惧。则其于有睹闻之时戒惧者。又可见矣。此子思言外之意。而戒惧所以为统体工夫者也。故朱子尝两论之。而于章句则合二说而释之曰。常存敬畏。先正臣金长生曰。戒惧是兼动静。今若专主静一边看。则恐有违朱夫子两看之意也。噫。性道教三字。是中庸三纲领。道一字。又是三纲领中纲领。故第二节。拈出一道字言之者此也。噫。情之目有七。而衍之则为七。约之则为四。故先儒有曰七情只是恶欲二字。又况爱属于喜。恶属于怒。而情只是性之欲。则只言四者于第四节。恐亦以此意。而三者之该于其中。亦可见矣。噫。性者心之理。而心只是气也。则所谓戒惧也。中和也。皆是言心之体用而气在其中。不言心而心已该焉。不言气而气已该焉。而朱子于序文。特言人心道心者。盖明性与心只是一般之义。而章句所谓鸢鱼也。鬼神也。亦莫非言气
问。详言偏全之异。而先正臣宋时烈有曰。章句槩言同得之性。而与或问合看然后得之。惟此一言。可以破甲乙之论也。噫。戒惧一节。或以为通动静言。或以为专属静一边。盖子思之言戒惧。乃在不睹闻之时。则不睹闻即未发时也。戒惧之属静。固子思之正意也。然不睹闻之时犹且戒惧。则其于有睹闻之时戒惧者。又可见矣。此子思言外之意。而戒惧所以为统体工夫者也。故朱子尝两论之。而于章句则合二说而释之曰。常存敬畏。先正臣金长生曰。戒惧是兼动静。今若专主静一边看。则恐有违朱夫子两看之意也。噫。性道教三字。是中庸三纲领。道一字。又是三纲领中纲领。故第二节。拈出一道字言之者此也。噫。情之目有七。而衍之则为七。约之则为四。故先儒有曰七情只是恶欲二字。又况爱属于喜。恶属于怒。而情只是性之欲。则只言四者于第四节。恐亦以此意。而三者之该于其中。亦可见矣。噫。性者心之理。而心只是气也。则所谓戒惧也。中和也。皆是言心之体用而气在其中。不言心而心已该焉。不言气而气已该焉。而朱子于序文。特言人心道心者。盖明性与心只是一般之义。而章句所谓鸢鱼也。鬼神也。亦莫非言气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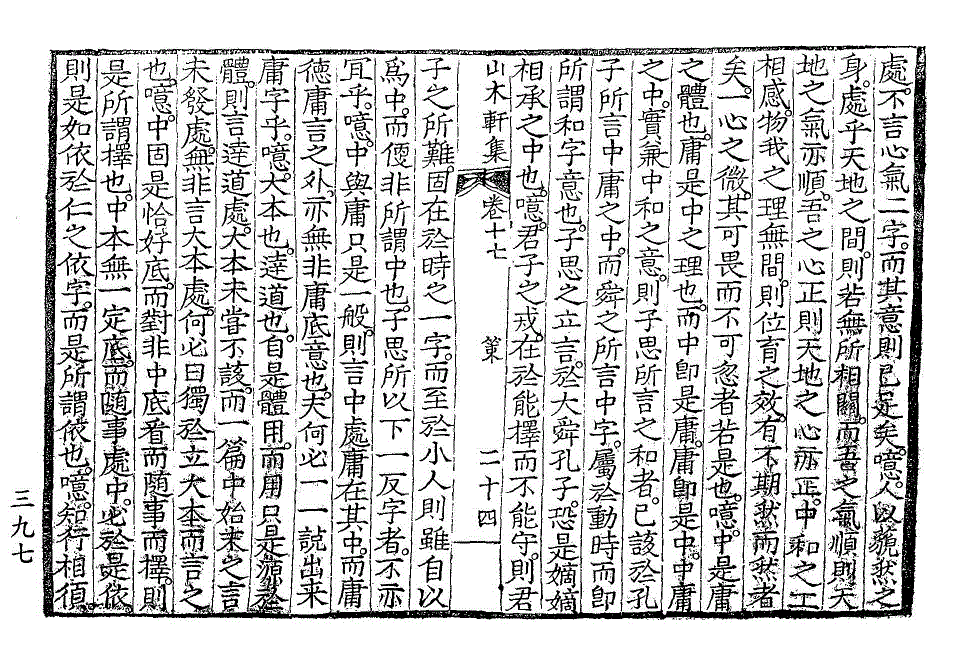 处。不言心气二字。而其意则已足矣。噫。人以藐然之身。处乎天地之间。则若无所相关。而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中和之工相感。物我之理无间。则位育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一心之微。其可畏而不可忽者若是也。噫。中是庸之体也。庸是中之理也。而中即是庸。庸即是中。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子思所言之和者。已该于孔子所言中庸之中。而舜之所言中字。属于动时而即所谓和字意也。子思之立言。于大舜孔子。恐是嫡嫡相承之中也。噫。君子之戒。在于能择而不能守。则君子之所难。固在于时之一字。而至于小人则虽自以为中。而便非所谓中也。子思所以下一反字者。不亦宜乎。噫。中与庸只是一般。则言中处庸在其中。而庸德庸言之外。亦无非庸底意也。夫何必一一说出来庸字乎。噫。大本也。达道也。自是体用。而用只是源于体。则言达道处。大本未尝不该。而一篇中始末之言未发处。无非言大本处。何必曰独于立大本而言之也。噫。中固是恰好底。而对非中底看而随事而择。则是所谓择也。中本无一定底。而随事处中。必于是依。则是如依于仁之依字。而是所谓依也。噫。知行相须。
处。不言心气二字。而其意则已足矣。噫。人以藐然之身。处乎天地之间。则若无所相关。而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中和之工相感。物我之理无间。则位育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一心之微。其可畏而不可忽者若是也。噫。中是庸之体也。庸是中之理也。而中即是庸。庸即是中。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则子思所言之和者。已该于孔子所言中庸之中。而舜之所言中字。属于动时而即所谓和字意也。子思之立言。于大舜孔子。恐是嫡嫡相承之中也。噫。君子之戒。在于能择而不能守。则君子之所难。固在于时之一字。而至于小人则虽自以为中。而便非所谓中也。子思所以下一反字者。不亦宜乎。噫。中与庸只是一般。则言中处庸在其中。而庸德庸言之外。亦无非庸底意也。夫何必一一说出来庸字乎。噫。大本也。达道也。自是体用。而用只是源于体。则言达道处。大本未尝不该。而一篇中始末之言未发处。无非言大本处。何必曰独于立大本而言之也。噫。中固是恰好底。而对非中底看而随事而择。则是所谓择也。中本无一定底。而随事处中。必于是依。则是如依于仁之依字。而是所谓依也。噫。知行相须。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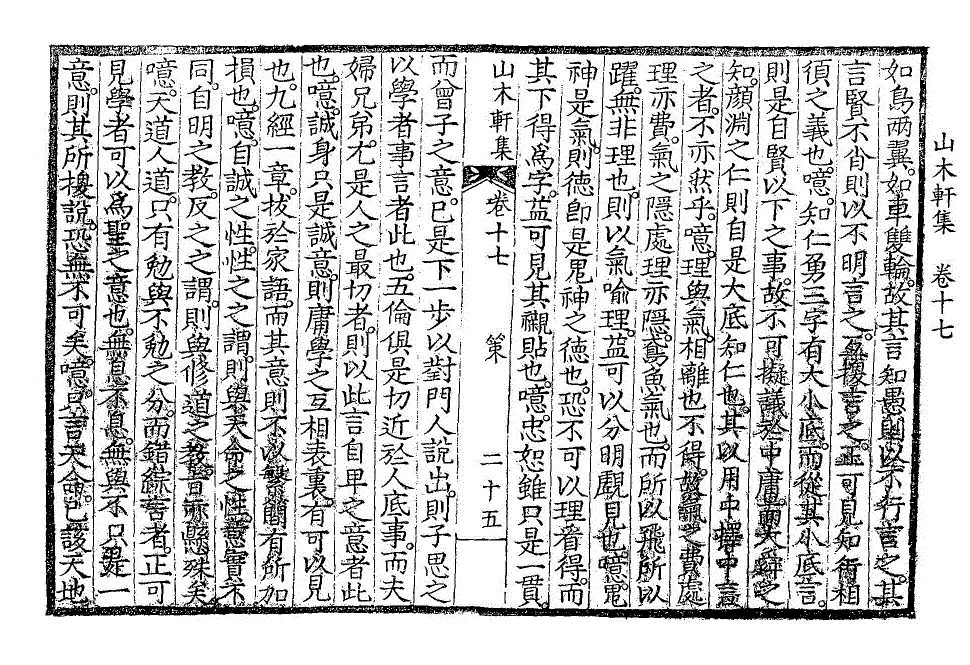 如鸟两翼。如车双轮。故其言知愚则以不行言之。其言贤不肖则以不明言之。互换言之。正可见知行相须之义也。噫。知仁勇三字有大小底。而从其小底言。则是自贤以下之事。故不可拟议于中庸。而大舜之知。颜渊之仁则自是大底知仁也。其以用中择中言之者。不亦然乎。噫。理与气。相离也不得。故气之费处理亦费。气之隐处理亦隐。鸢鱼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无非理也。则以气喻理。益可以分明觑见也。噫。鬼神是气。则德即是鬼神之德也。恐不可以理看得。而其下得为字。益可见其衬贴也。噫。忠恕虽只是一贯。而曾子之意。已是下一步以对门人说出。则子思之以学者事言者此也。五伦俱是切近于人底事。而夫妇兄弟。尤是人之最切者。则以此言自卑之意者此也。噫。诚身只是诚意。则庸学之互相表里。有可以见也。九经一章。拔于家语。而其意则不以繁简有所加损也。噫。自诚之性。性之之谓。则与天命之性。意实不同。自明之教。反之之谓。则与修道之教。旨亦悬殊矣。噫。天道人道。只有勉与不勉之分。而错综言者。正可见学者可以为圣之意也。无息不息。无与不只是一意。则其所换说。恐无不可矣。噫。只言天命。已该天地
如鸟两翼。如车双轮。故其言知愚则以不行言之。其言贤不肖则以不明言之。互换言之。正可见知行相须之义也。噫。知仁勇三字有大小底。而从其小底言。则是自贤以下之事。故不可拟议于中庸。而大舜之知。颜渊之仁则自是大底知仁也。其以用中择中言之者。不亦然乎。噫。理与气。相离也不得。故气之费处理亦费。气之隐处理亦隐。鸢鱼气也。而所以飞所以跃。无非理也。则以气喻理。益可以分明觑见也。噫。鬼神是气。则德即是鬼神之德也。恐不可以理看得。而其下得为字。益可见其衬贴也。噫。忠恕虽只是一贯。而曾子之意。已是下一步以对门人说出。则子思之以学者事言者此也。五伦俱是切近于人底事。而夫妇兄弟。尤是人之最切者。则以此言自卑之意者此也。噫。诚身只是诚意。则庸学之互相表里。有可以见也。九经一章。拔于家语。而其意则不以繁简有所加损也。噫。自诚之性。性之之谓。则与天命之性。意实不同。自明之教。反之之谓。则与修道之教。旨亦悬殊矣。噫。天道人道。只有勉与不勉之分。而错综言者。正可见学者可以为圣之意也。无息不息。无与不只是一意。则其所换说。恐无不可矣。噫。只言天命。已该天地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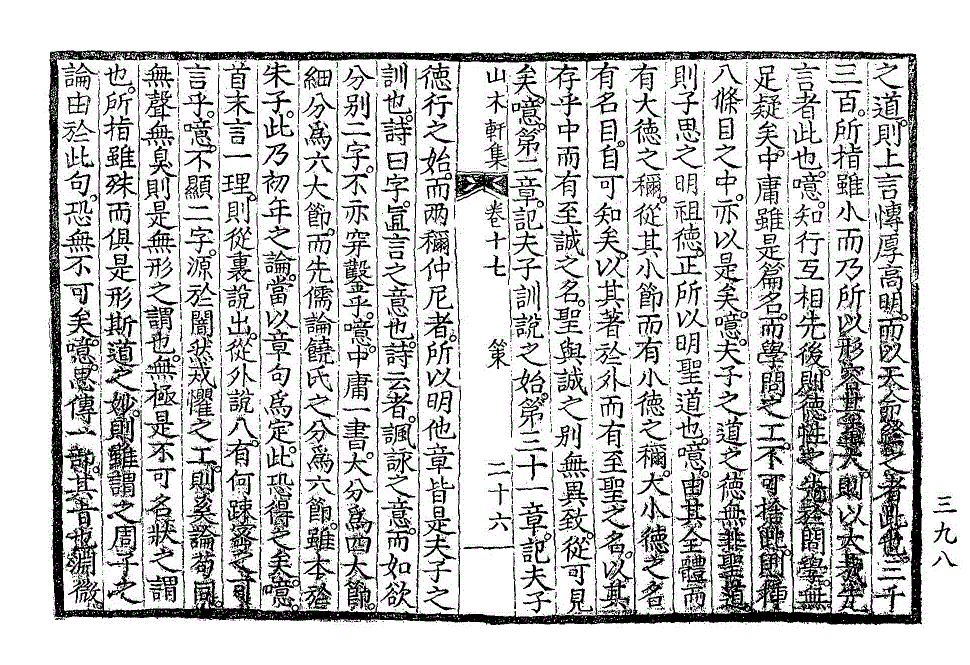 之道。则上言博厚高明。而以天命终之者此也。三千三百。所指虽小而乃所以形容其至大。则以大哉先言者此也。噫。知行互相先后。则德性之先于问学。无足疑矣。中庸虽是篇名。而学问之工。不可舍此。则插八条目之中。亦以是矣。噫。夫子之道之德无非圣道。则子思之明祖德。正所以明圣道也。噫。由其全体而有大德之称。从其小节而有小德之称。大小德之名有名目。自可知矣。以其著于外而有至圣之名。以其存乎中而有至诚之名。圣与诚之别无异致。从可见矣。噫。第二章。记夫子训说之始。第三十一章。记夫子德行之始。而两称仲尼者。所以明他章皆是夫子之训也。诗曰字。直言之意也。诗云者。讽咏之意。而如欲分别二字。不亦穿凿乎。噫。中庸一书。大分为四大节。细分为六大节。而先儒论饶氏之分为六节。虽本于朱子。此乃初年之论。当以章句为定。此恐得之矣。噫。首末言一理。则从里说出。从外说入。有何疏密之可言乎。噫。不显二字。源于闇然戒惧之工。则奚论苟同。无声无臭则是无形之谓也。无极是不可名状之谓也。所指虽殊而俱是形斯道之妙。则虽谓之周子之论由于此句。恐无不可矣。噫。思传一部。其旨也渊微。
之道。则上言博厚高明。而以天命终之者此也。三千三百。所指虽小而乃所以形容其至大。则以大哉先言者此也。噫。知行互相先后。则德性之先于问学。无足疑矣。中庸虽是篇名。而学问之工。不可舍此。则插八条目之中。亦以是矣。噫。夫子之道之德无非圣道。则子思之明祖德。正所以明圣道也。噫。由其全体而有大德之称。从其小节而有小德之称。大小德之名有名目。自可知矣。以其著于外而有至圣之名。以其存乎中而有至诚之名。圣与诚之别无异致。从可见矣。噫。第二章。记夫子训说之始。第三十一章。记夫子德行之始。而两称仲尼者。所以明他章皆是夫子之训也。诗曰字。直言之意也。诗云者。讽咏之意。而如欲分别二字。不亦穿凿乎。噫。中庸一书。大分为四大节。细分为六大节。而先儒论饶氏之分为六节。虽本于朱子。此乃初年之论。当以章句为定。此恐得之矣。噫。首末言一理。则从里说出。从外说入。有何疏密之可言乎。噫。不显二字。源于闇然戒惧之工。则奚论苟同。无声无臭则是无形之谓也。无极是不可名状之谓也。所指虽殊而俱是形斯道之妙。则虽谓之周子之论由于此句。恐无不可矣。噫。思传一部。其旨也渊微。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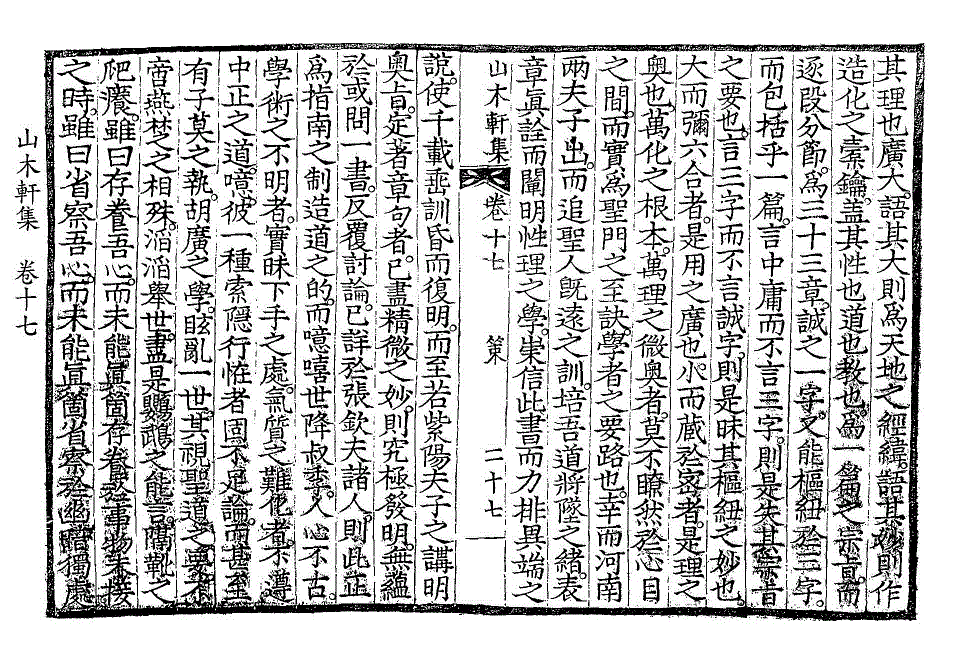 其理也广大。语其大则为天地之经纬。语其妙则作造化之橐钥。盖其性也道也教也。为一篇之宗旨。而逐段分节。为三十三章。诚之一字。又能枢纽于三字。而包括乎一篇。言中庸而不言三字。则是失其宗旨之要也。言三字而不言诚字。则是昧其枢纽之妙也。大而弥六合者。是用之广也。小而藏于密者。是理之奥也。万化之根本。万理之微奥者。莫不瞭然于心目之间。而实为圣门之至诀。学者之要路也。幸而河南两夫子出。而追圣人既远之训。培吾道将坠之绪。表章真诠而阐明性理之学。崇信此书而力排异端之说。使千载垂训昏而复明。而至若紫阳夫子之讲明奥旨。定著章句者。已尽精微之妙。则究极发明。无蕴于或问一书。反覆讨论。已详于张钦夫诸人。则此正为指南之制造道之的。而噫嘻世降叔季。人心不古。学(彳+米+亍)之不明者。实昧下手之处。气质之难化者。不遵中正之道。噫。彼一种索隐行怪者固不足论。而甚至有子莫之执。胡广之学。眩乱一世。其视圣道之要。不啻燕楚之相殊。滔滔举世。尽是鹦鹉之能言。隔靴之爬痒。虽曰存养吾心。而未能真个存养于事物未接之时。虽曰省察吾心。而未能真个省察于幽暗独处
其理也广大。语其大则为天地之经纬。语其妙则作造化之橐钥。盖其性也道也教也。为一篇之宗旨。而逐段分节。为三十三章。诚之一字。又能枢纽于三字。而包括乎一篇。言中庸而不言三字。则是失其宗旨之要也。言三字而不言诚字。则是昧其枢纽之妙也。大而弥六合者。是用之广也。小而藏于密者。是理之奥也。万化之根本。万理之微奥者。莫不瞭然于心目之间。而实为圣门之至诀。学者之要路也。幸而河南两夫子出。而追圣人既远之训。培吾道将坠之绪。表章真诠而阐明性理之学。崇信此书而力排异端之说。使千载垂训昏而复明。而至若紫阳夫子之讲明奥旨。定著章句者。已尽精微之妙。则究极发明。无蕴于或问一书。反覆讨论。已详于张钦夫诸人。则此正为指南之制造道之的。而噫嘻世降叔季。人心不古。学(彳+米+亍)之不明者。实昧下手之处。气质之难化者。不遵中正之道。噫。彼一种索隐行怪者固不足论。而甚至有子莫之执。胡广之学。眩乱一世。其视圣道之要。不啻燕楚之相殊。滔滔举世。尽是鹦鹉之能言。隔靴之爬痒。虽曰存养吾心。而未能真个存养于事物未接之时。虽曰省察吾心。而未能真个省察于幽暗独处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3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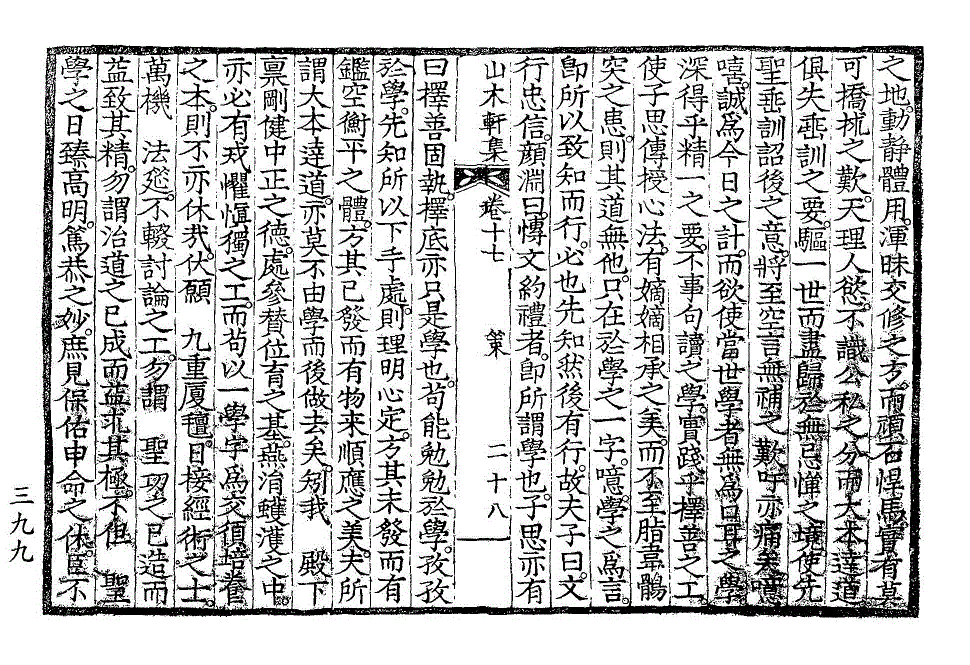 之地。动静体用。浑昧交修之方。而顽石悍马。实有莫可挢救之叹。天理人欲。不识公私之分而大本达道。俱失垂训之要。驱一世而尽归于无忌惮之境。使先圣垂训诏后之意。将至空言无补之叹。吁亦痛矣。噫嘻。诚为今日之计。而欲使当世学者无为口耳之学。深得乎精一之要。不事句读之学。实践乎择善之工。使子思传授心法。有嫡嫡相承之美。而不至脂韦鹘突之患。则其道无他。只在于学之一字。噫。学之为言。即所以致知而行。必也先知然后有行。故夫子曰。文行忠信。颜渊曰。博文约礼者。即所谓学也。子思亦有曰择善固执。择底亦只是学也。苟能勉勉于学。孜孜于学。先知所以下手处。则理明心定。方其未发而有鉴空衡平之体。方其已发而有物来顺应之美。夫所谓大本达道。亦莫不由学而后做去矣。矧我 殿下禀刚健中正之德。处参赞位育之基。燕涓蠖濩之中。亦必有戒惧慎独之工。而苟以一学字为交须培养之本。则不亦休哉。伏愿 九重厦毡。日接经术之士。万机 法筵。不辍讨论之工。勿谓 圣功之已造而益致其精。勿谓治道之已成而益求其极。不但 圣学之日臻高明。笃恭之妙。庶见保佑申命之休。臣不
之地。动静体用。浑昧交修之方。而顽石悍马。实有莫可挢救之叹。天理人欲。不识公私之分而大本达道。俱失垂训之要。驱一世而尽归于无忌惮之境。使先圣垂训诏后之意。将至空言无补之叹。吁亦痛矣。噫嘻。诚为今日之计。而欲使当世学者无为口耳之学。深得乎精一之要。不事句读之学。实践乎择善之工。使子思传授心法。有嫡嫡相承之美。而不至脂韦鹘突之患。则其道无他。只在于学之一字。噫。学之为言。即所以致知而行。必也先知然后有行。故夫子曰。文行忠信。颜渊曰。博文约礼者。即所谓学也。子思亦有曰择善固执。择底亦只是学也。苟能勉勉于学。孜孜于学。先知所以下手处。则理明心定。方其未发而有鉴空衡平之体。方其已发而有物来顺应之美。夫所谓大本达道。亦莫不由学而后做去矣。矧我 殿下禀刚健中正之德。处参赞位育之基。燕涓蠖濩之中。亦必有戒惧慎独之工。而苟以一学字为交须培养之本。则不亦休哉。伏愿 九重厦毡。日接经术之士。万机 法筵。不辍讨论之工。勿谓 圣功之已造而益致其精。勿谓治道之已成而益求其极。不但 圣学之日臻高明。笃恭之妙。庶见保佑申命之休。臣不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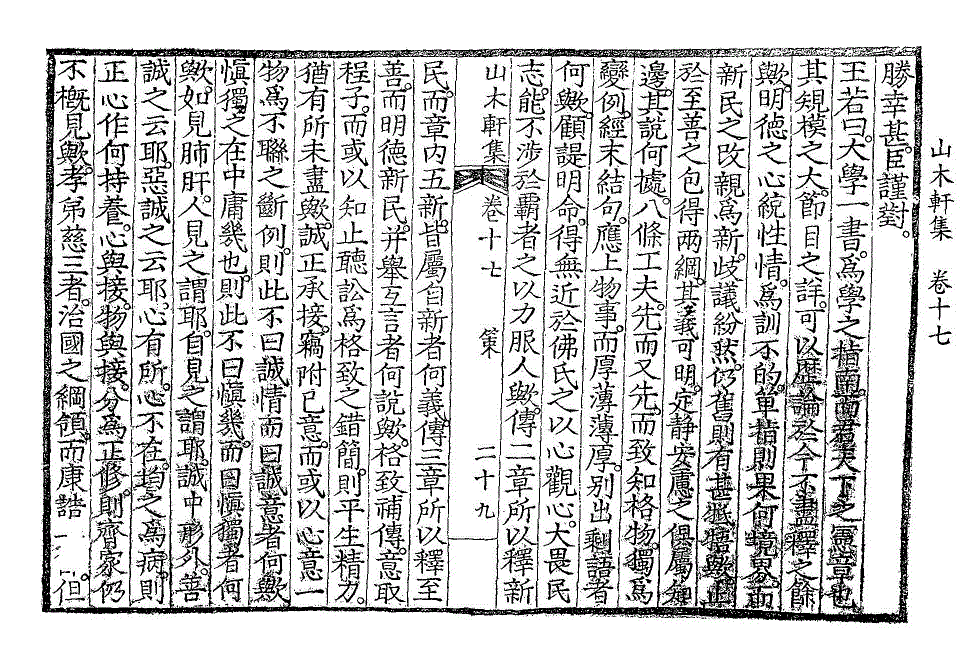 胜幸甚。臣谨对。
胜幸甚。臣谨对。[大学书]
王若曰。大学一书。为学之指南。而君天下之宪章也。其规模之大。节目之详。可以历论于今不尽释之馀欤。明德之心统性情。为训不的。单指则果何境界。而新民之改亲为新。歧议纷然。仍旧则有甚牴牾欤。止于至善之包得两纲。其义可明。定静安虑之俱属知边。其说何据。八条工夫。先而又先。而致知格物。独为变例。经末结句。应上物事。而厚薄薄厚。别出剩语者何欤。顾諟明命。得无近于佛氏之以心观心。大畏民志。能不涉于霸者之以力服人欤。传二章所以释新民。而章内五新。皆属自新者何义。传三章所以释至善。而明德新民。并举互言者何说欤。格致补传。意取程子。而或以知止听讼为格致之错简。则平生精力。犹有所未尽欤。诚正承接。窃附己意。而或以心意一物为不联之断例。则此不曰诚情而曰诚意者何欤。慎独之在中庸几也。则此不曰慎几。而曰慎独者何欤。如见肺肝。人见之谓耶。自见之谓耶。诚中形外。善诚之云耶。恶诚之云耶。心有所。心不在。均之为病。则正心作何持养。心与接。物与接。分为正修。则齐家仍不概见欤。孝弟慈三者。治国之纲领。而康诰一节。但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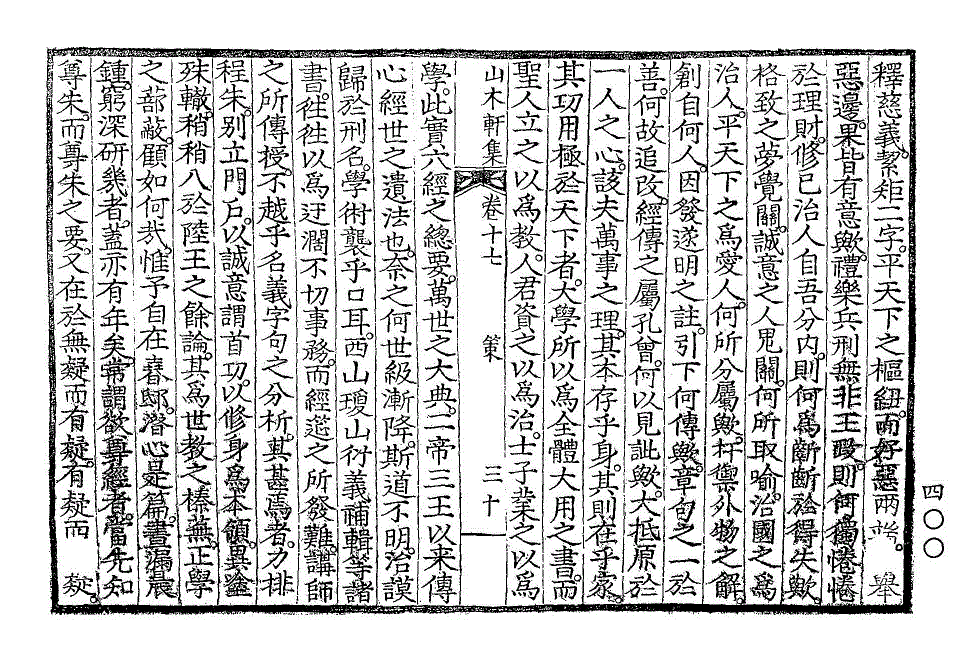 释慈义。絜矩二字。平天下之枢纽。而好恶两端。▣(一作只)举恶边。果皆有意欤。礼乐兵刑无非王政。则何独惓惓于理财。修己治人自吾分内。则何为龂龂于得失欤。格致之梦觉关。诚意之人鬼关。何所取喻。治国之为治人。平天下之为爱人。何所分属欤。捍御外物之解。创自何人。因发遂明之注。引下何传欤。章句之一于善。何故追改。经传之属孔曾。何以见訾欤。大抵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其本存乎身。其则在乎家。其功用极于天下者。大学所以为全体大用之书。而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资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此实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奈之何世级渐降。斯道不明。治谟归于刑名。学术袭乎口耳。西山琼山衍义补辑等诸书。往往以为迂阔不切事务。而经筵之所发难。讲师之所传授。不越乎名义字句之分析。其甚焉者。力排程朱。别立门户。以诚意谓首功。以修身为本领。异涂殊辙。稍稍入于陆王之馀论。其为世教之榛芜。正学之蔀蔽。顾如何哉。惟予自在春邸。潜心是篇。昼漏晨钟。穷深研几者。盖亦有年矣。常谓欲尊经者。当先知尊朱。而尊朱之要。又在于无疑而有疑。有疑而无疑。
释慈义。絜矩二字。平天下之枢纽。而好恶两端。▣(一作只)举恶边。果皆有意欤。礼乐兵刑无非王政。则何独惓惓于理财。修己治人自吾分内。则何为龂龂于得失欤。格致之梦觉关。诚意之人鬼关。何所取喻。治国之为治人。平天下之为爱人。何所分属欤。捍御外物之解。创自何人。因发遂明之注。引下何传欤。章句之一于善。何故追改。经传之属孔曾。何以见訾欤。大抵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其本存乎身。其则在乎家。其功用极于天下者。大学所以为全体大用之书。而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资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此实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奈之何世级渐降。斯道不明。治谟归于刑名。学术袭乎口耳。西山琼山衍义补辑等诸书。往往以为迂阔不切事务。而经筵之所发难。讲师之所传授。不越乎名义字句之分析。其甚焉者。力排程朱。别立门户。以诚意谓首功。以修身为本领。异涂殊辙。稍稍入于陆王之馀论。其为世教之榛芜。正学之蔀蔽。顾如何哉。惟予自在春邸。潜心是篇。昼漏晨钟。穷深研几者。盖亦有年矣。常谓欲尊经者。当先知尊朱。而尊朱之要。又在于无疑而有疑。有疑而无疑。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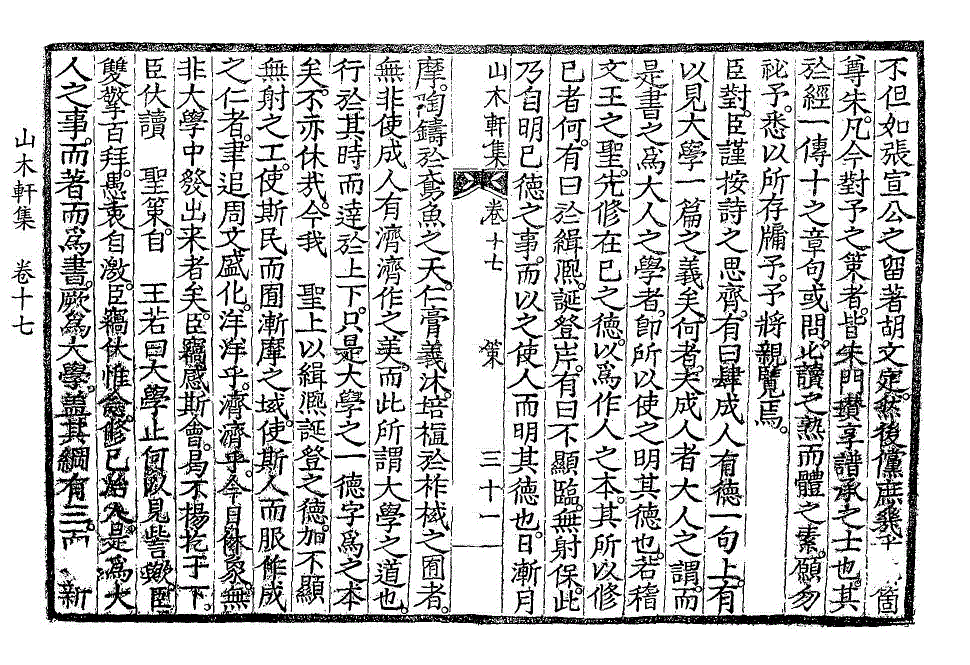 不但如张宣公之留著胡文定。然后傥庶几乎真个尊朱。凡今对予之策者。皆朱门瓒享谱承之士也。其于经一传十之章句或问。必读之熟而体之素。愿勿秘予。悉以所存牖予。予将亲览焉。
不但如张宣公之留著胡文定。然后傥庶几乎真个尊朱。凡今对予之策者。皆朱门瓒享谱承之士也。其于经一传十之章句或问。必读之熟而体之素。愿勿秘予。悉以所存牖予。予将亲览焉。臣对。臣谨按诗之思齐。有曰肆成人有德一句上。有以见大学一篇之义矣。何者。夫成人者大人之谓。而是书之为大人之学者。即所以使之明其德也。若稽文王之圣。先修在己之德。以为作人之本。其所以修己者何。有曰于缉熙。诞登岸。有曰不显临。无射保。此乃自明己德之事。而以之使人而明其德也。日渐月摩。陶铸于鸢鱼之天。仁膏义沐。培植于柞棫之囿者。无非使成人有济济作之美。而此所谓大学之道也。行于其时而达于上下。只是大学之一德字为之本矣。不亦休哉。今我 圣上以缉熙诞登之德。加不显无射之工。使斯民而囿渐摩之域。使斯人而服作成之仁者。聿追周文盛化。洋洋乎。济济乎。今日休象。无非大学中发出来者矣。臣窃感斯会。曷不扬扢于下。臣伏读 圣策。自 王若曰大学止何以见訾欤。臣双擎百拜。愚衷自激。臣窃伏惟念。修己治大。是为大人之事。而著而为书。厥为大学。盖其纲有三。而明新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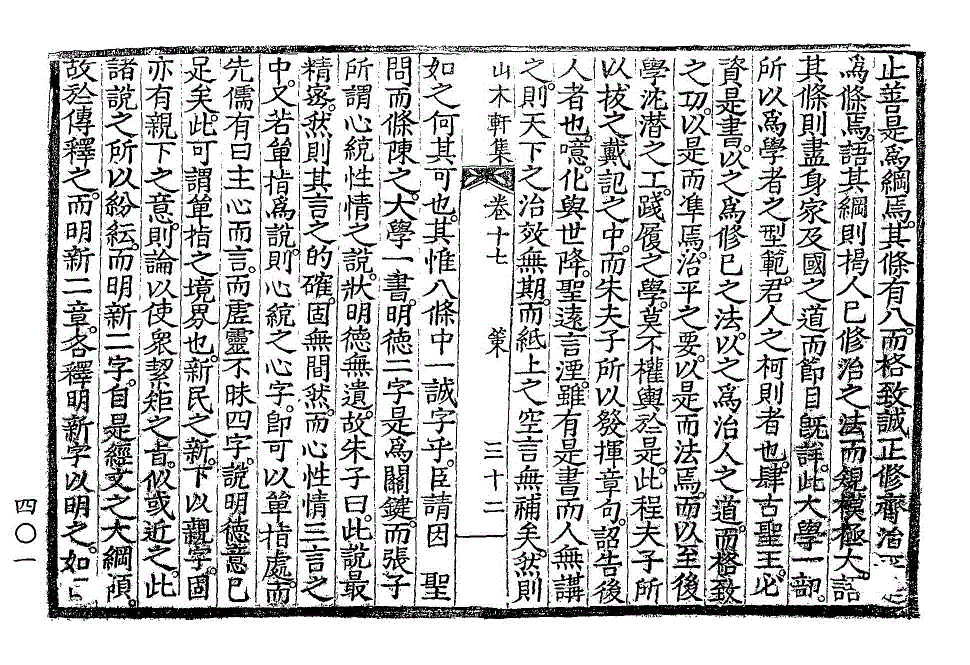 止善是为纲焉。其条有八。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为条焉。语其纲则揭人己修治之法而规模极大。语其条则尽身家及国之道而节目既详。此大学一部。所以为学者之型范。君人之柯则者也。肆古圣王。必资是书。以之为修己之法。以之为治人之道。而格致之功。以是而准焉。治平之要。以是而法焉。而以至后学沈潜之工。践履之学。莫不权舆于是。此程夫子所以拔之戴记之中。而朱夫子所以发挥章句。诏告后人者也。噫。化与世降。圣远言湮。虽有是书而人无讲之。则天下之治效无期。而纸上之空言无补矣。然则如之何其可也。其惟八条中一诚字乎。臣请因 圣问而条陈之。大学一书。明德二字是为关键。而张子所谓心统性情之说。状明德无遗。故朱子曰。此说最精密。然则其言之的确。固无间然。而心性情三言之中。又若单指为说。则心统之心字。即可以单指处。而先儒有曰主心而言。而虚灵不昧四字。说明德意已足矣。此可谓单指之境界也。新民之新。下以亲字。固亦有亲下之意。则论以使众絜矩之旨。似或近之。此诸说之所以纷纭。而明新二字。自是经文之大纲领。故于传释之。而明新二章。各释明新字以明之。如曰
止善是为纲焉。其条有八。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为条焉。语其纲则揭人己修治之法而规模极大。语其条则尽身家及国之道而节目既详。此大学一部。所以为学者之型范。君人之柯则者也。肆古圣王。必资是书。以之为修己之法。以之为治人之道。而格致之功。以是而准焉。治平之要。以是而法焉。而以至后学沈潜之工。践履之学。莫不权舆于是。此程夫子所以拔之戴记之中。而朱夫子所以发挥章句。诏告后人者也。噫。化与世降。圣远言湮。虽有是书而人无讲之。则天下之治效无期。而纸上之空言无补矣。然则如之何其可也。其惟八条中一诚字乎。臣请因 圣问而条陈之。大学一书。明德二字是为关键。而张子所谓心统性情之说。状明德无遗。故朱子曰。此说最精密。然则其言之的确。固无间然。而心性情三言之中。又若单指为说。则心统之心字。即可以单指处。而先儒有曰主心而言。而虚灵不昧四字。说明德意已足矣。此可谓单指之境界也。新民之新。下以亲字。固亦有亲下之意。则论以使众絜矩之旨。似或近之。此诸说之所以纷纭。而明新二字。自是经文之大纲领。故于传释之。而明新二章。各释明新字以明之。如曰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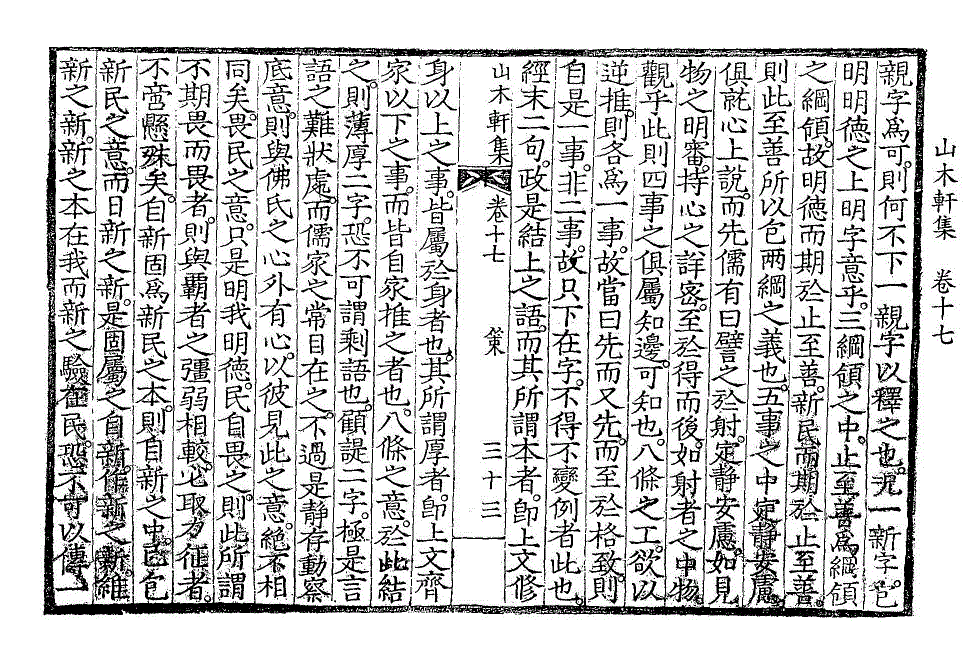 亲字为可。则何不下一亲字以释之也。况一新字。包明明德之上明字意乎。三纲领之中。止至善为纲领之纲领。故明德而期于止至善。新民而期于止至善。则此至善所以包两纲之义也。五事之中定静安虑。俱就心上说。而先儒有曰譬之于射。定静安虑。如见物之明审。持心之详密。至于得而后。如射者之中物。观乎此则四事之俱属知边。可知也。八条之工。欲以逆推。则各为一事。故当曰先而又先。而至于格致。则自是一事。非二事。故只下在字。不得不变例者此也。经末二句。政是结上之语。而其所谓本者。即上文修身以上之事。皆属于身者也。其所谓厚者。即上文齐家以下之事。而皆自家推之者也。八条之意。于此结之。则薄厚二字。恐不可谓剩语也。顾諟二字。极是言语之难状处。而儒家之常目在之。不过是静存动察底意。则与佛氏之心外有心。以彼见此之意。绝不相同矣。畏民之意。只是明我明德。民自畏之。则此所谓不期畏而畏者。则与霸者之彊弱相较。必取力征者。不啻悬殊矣。自新固为新民之本。则自新之中。已包新民之意。而日新之新。是固属之自新。作新之新。维新之新。新之本在我而新之验在民。恐不可以传一
亲字为可。则何不下一亲字以释之也。况一新字。包明明德之上明字意乎。三纲领之中。止至善为纲领之纲领。故明德而期于止至善。新民而期于止至善。则此至善所以包两纲之义也。五事之中定静安虑。俱就心上说。而先儒有曰譬之于射。定静安虑。如见物之明审。持心之详密。至于得而后。如射者之中物。观乎此则四事之俱属知边。可知也。八条之工。欲以逆推。则各为一事。故当曰先而又先。而至于格致。则自是一事。非二事。故只下在字。不得不变例者此也。经末二句。政是结上之语。而其所谓本者。即上文修身以上之事。皆属于身者也。其所谓厚者。即上文齐家以下之事。而皆自家推之者也。八条之意。于此结之。则薄厚二字。恐不可谓剩语也。顾諟二字。极是言语之难状处。而儒家之常目在之。不过是静存动察底意。则与佛氏之心外有心。以彼见此之意。绝不相同矣。畏民之意。只是明我明德。民自畏之。则此所谓不期畏而畏者。则与霸者之彊弱相较。必取力征者。不啻悬殊矣。自新固为新民之本。则自新之中。已包新民之意。而日新之新。是固属之自新。作新之新。维新之新。新之本在我而新之验在民。恐不可以传一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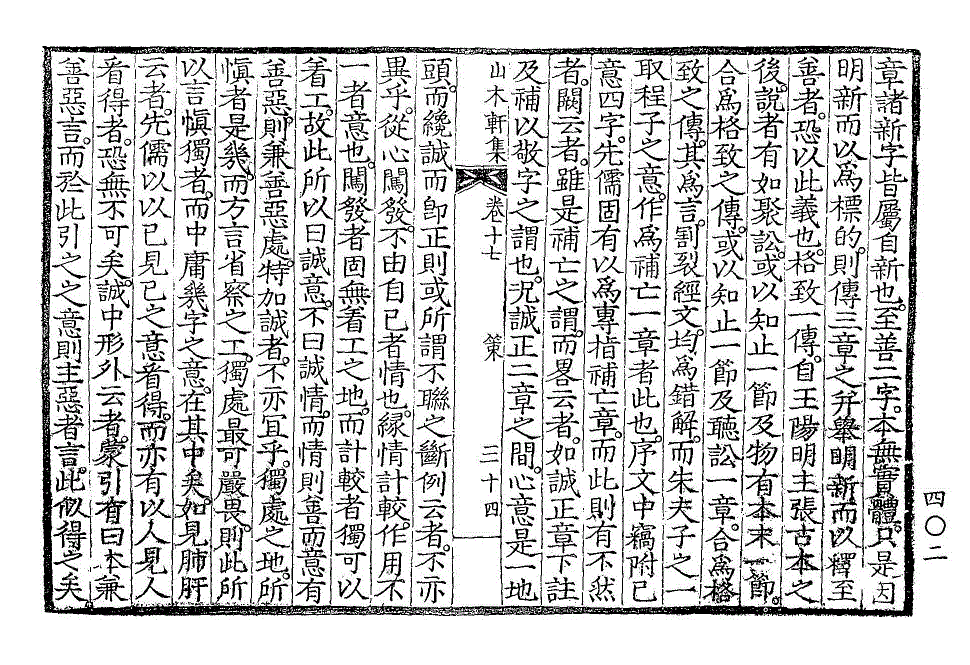 章诸新字皆属自新也。至善二字。本无实体。只是因明新而以为标的。则传三章之并举明新而以释至善者。恐以此义也。格致一传。自王阳明主张古本之后。说者有如聚讼。或以知止一节及物有本末一节。合为格致之传。或以知止一节及听讼一章。合为格致之传。其为言。割裂经文。均为错解。而朱夫子之一取程子之意。作为补亡一章者此也。序文中窃附己意四字。先儒固有以为专指补亡章。而此则有不然者。阙云者。虽是补亡之谓。而略云者。如诚正章下注及补以敬字之谓也。况诚正二章之间。心意是一地头。而才诚而即正则或所谓不联之断例云者。不亦异乎。从心闯发。不由自己者情也。缘情计较。作用不一者意也。闯发者固无着工之地。而计较者独可以着工。故此所以曰诚意。不曰诚情。而情则善而意有善恶。则兼善恶处。特加诚者。不亦宜乎。独处之地。所慎者是几。而方言省察之工。独处最可严畏。则此所以言慎独者。而中庸几字之意。在其中矣。如见肺肝云者。先儒以以己见己之意看得。而亦有以人见人看得者。恐无不可矣。诚中形外云者。蒙引有曰本兼善恶言。而于此引之之意则主恶者言。此似得之矣。
章诸新字皆属自新也。至善二字。本无实体。只是因明新而以为标的。则传三章之并举明新而以释至善者。恐以此义也。格致一传。自王阳明主张古本之后。说者有如聚讼。或以知止一节及物有本末一节。合为格致之传。或以知止一节及听讼一章。合为格致之传。其为言。割裂经文。均为错解。而朱夫子之一取程子之意。作为补亡一章者此也。序文中窃附己意四字。先儒固有以为专指补亡章。而此则有不然者。阙云者。虽是补亡之谓。而略云者。如诚正章下注及补以敬字之谓也。况诚正二章之间。心意是一地头。而才诚而即正则或所谓不联之断例云者。不亦异乎。从心闯发。不由自己者情也。缘情计较。作用不一者意也。闯发者固无着工之地。而计较者独可以着工。故此所以曰诚意。不曰诚情。而情则善而意有善恶。则兼善恶处。特加诚者。不亦宜乎。独处之地。所慎者是几。而方言省察之工。独处最可严畏。则此所以言慎独者。而中庸几字之意。在其中矣。如见肺肝云者。先儒以以己见己之意看得。而亦有以人见人看得者。恐无不可矣。诚中形外云者。蒙引有曰本兼善恶言。而于此引之之意则主恶者言。此似得之矣。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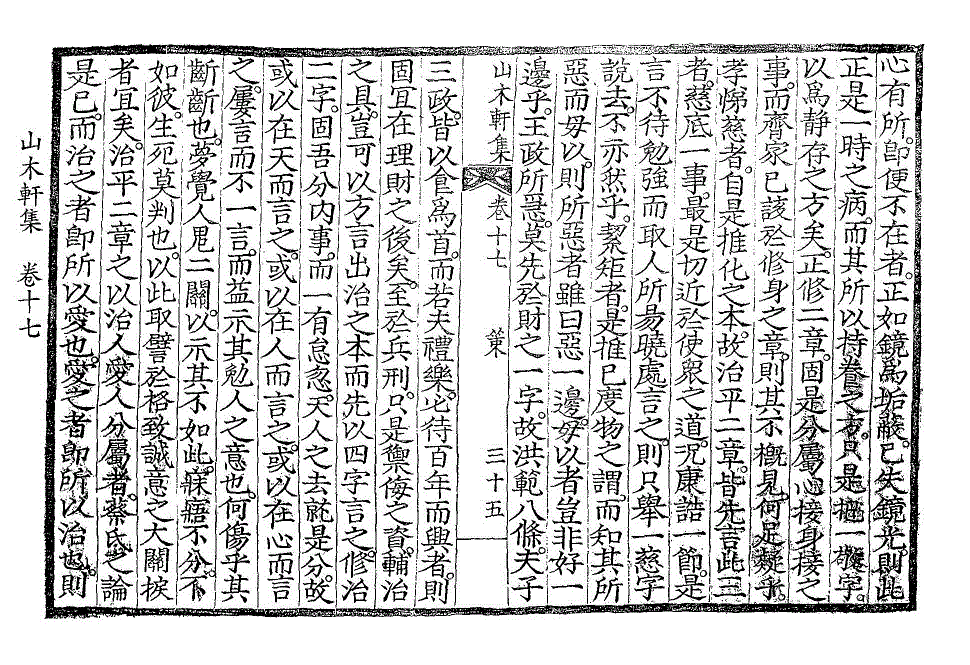 心有所。即便不在者。正如镜为垢蔽。已失镜光。则此正是一时之病。而其所以持养之方。只是把一敬字。以为静存之方矣。正修二章。固是分属心接身接之事。而齐家已该于修身之章。则其不概见。何足疑乎。孝悌慈者。自是推化之本。故治平二章。皆先言此三者。慈底一事。最是切近于使众之道。况康诰一节。是言不待勉强而取人所易晓处言之。则只举一慈字说去。不亦然乎。絜矩者。是推己度物之谓。而知其所恶而毋以。则所恶者虽曰恶一边。毋以者岂非好一边乎。王政所急。莫先于财之一字。故洪范八条。夫子三政。皆以食为首。而若夫礼乐。必待百年而兴者。则固宜在理财之后矣。至于兵刑。只是御侮之资。辅治之具。岂可以方言出治之本而先以四字言之。修治二字。固吾分内事。而一有怠忽。天人之去就是分。故或以在天而言之。或以在人而言之。或以在心而言之。屡言而不一言。而益示其勉人之意也。何伤乎其龂龂也。梦觉人鬼二关。以示其不如此。寐寤不分。不如彼。生死莫判也。以此取譬于格致诚意之大关捩者宜矣。治平二章之以治人爱人分属者。蔡氏之论是已。而治之者即所以爱也。爱之者即所以治也。则
心有所。即便不在者。正如镜为垢蔽。已失镜光。则此正是一时之病。而其所以持养之方。只是把一敬字。以为静存之方矣。正修二章。固是分属心接身接之事。而齐家已该于修身之章。则其不概见。何足疑乎。孝悌慈者。自是推化之本。故治平二章。皆先言此三者。慈底一事。最是切近于使众之道。况康诰一节。是言不待勉强而取人所易晓处言之。则只举一慈字说去。不亦然乎。絜矩者。是推己度物之谓。而知其所恶而毋以。则所恶者虽曰恶一边。毋以者岂非好一边乎。王政所急。莫先于财之一字。故洪范八条。夫子三政。皆以食为首。而若夫礼乐。必待百年而兴者。则固宜在理财之后矣。至于兵刑。只是御侮之资。辅治之具。岂可以方言出治之本而先以四字言之。修治二字。固吾分内事。而一有怠忽。天人之去就是分。故或以在天而言之。或以在人而言之。或以在心而言之。屡言而不一言。而益示其勉人之意也。何伤乎其龂龂也。梦觉人鬼二关。以示其不如此。寐寤不分。不如彼。生死莫判也。以此取譬于格致诚意之大关捩者宜矣。治平二章之以治人爱人分属者。蔡氏之论是已。而治之者即所以爱也。爱之者即所以治也。则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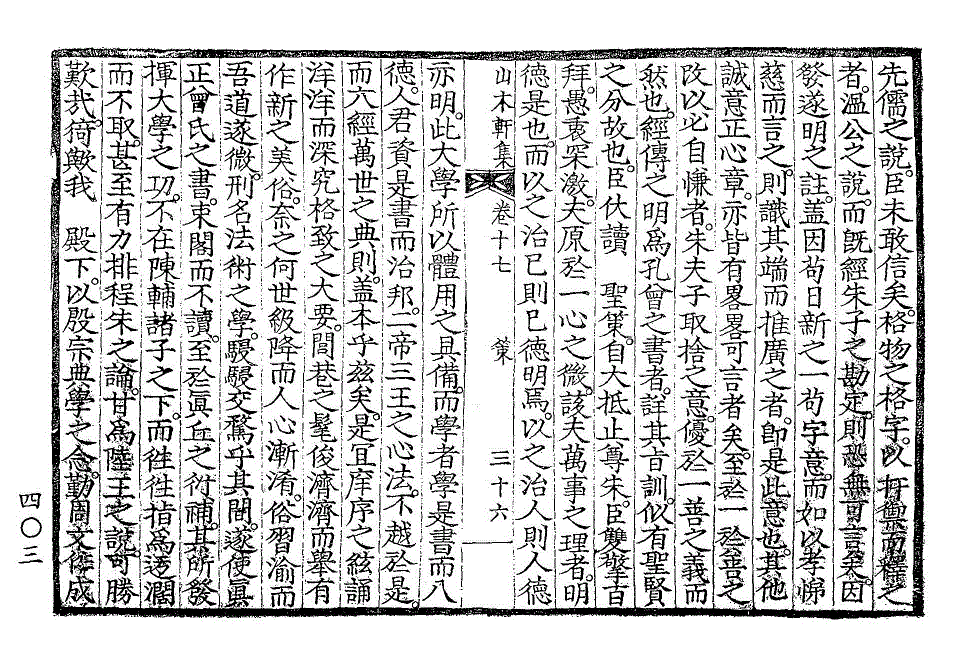 先儒之说。臣未敢信矣。格物之格字。以捍御而释之者。温公之说。而既经朱子之勘定。则恐无可言矣。因发遂明之注。盖因苟日新之一苟字意。而如以孝悌慈而言之。则识其端而推广之者。即是此意也。其他诚意正心章。亦皆有略略可言者矣。至于一于善之改以必自慊者。朱夫子取舍之意。优于一善之义而然也。经传之明为孔曾之书者。详其旨训。似有圣贤之分故也。臣伏读 圣策。自大抵止尊朱。臣双擎百拜。愚衷深激。夫原于一心之微。该夫万事之理者。明德是也。而以之治己则己德明焉。以之治人则人德亦明。此大学所以体用之具备。而学者学是书而入德。人君资是书而治邦。二帝三王之心法。不越于是。而六经万世之典则。盖本乎玆矣。是宜庠序之弦诵洋洋而深究格致之大要。闾巷之髦俊济济而举有作新之美俗。奈之何世级降而人心渐淆。俗习渝而吾道遂微。刑名法(彳+米+亍)之学。骎骎交骛乎其间。遂使真正曾氏之书。束阁而不读。至于真丘之衍补。其所发挥大学之功。不在陈辅诸子之下。而往往指为迂阔而不取。甚至有力排程朱之论。甘为陆王之说。可胜叹哉。猗欤我 殿下。以殷宗典学之念。勤周文作成
先儒之说。臣未敢信矣。格物之格字。以捍御而释之者。温公之说。而既经朱子之勘定。则恐无可言矣。因发遂明之注。盖因苟日新之一苟字意。而如以孝悌慈而言之。则识其端而推广之者。即是此意也。其他诚意正心章。亦皆有略略可言者矣。至于一于善之改以必自慊者。朱夫子取舍之意。优于一善之义而然也。经传之明为孔曾之书者。详其旨训。似有圣贤之分故也。臣伏读 圣策。自大抵止尊朱。臣双擎百拜。愚衷深激。夫原于一心之微。该夫万事之理者。明德是也。而以之治己则己德明焉。以之治人则人德亦明。此大学所以体用之具备。而学者学是书而入德。人君资是书而治邦。二帝三王之心法。不越于是。而六经万世之典则。盖本乎玆矣。是宜庠序之弦诵洋洋而深究格致之大要。闾巷之髦俊济济而举有作新之美俗。奈之何世级降而人心渐淆。俗习渝而吾道遂微。刑名法(彳+米+亍)之学。骎骎交骛乎其间。遂使真正曾氏之书。束阁而不读。至于真丘之衍补。其所发挥大学之功。不在陈辅诸子之下。而往往指为迂阔而不取。甚至有力排程朱之论。甘为陆王之说。可胜叹哉。猗欤我 殿下。以殷宗典学之念。勤周文作成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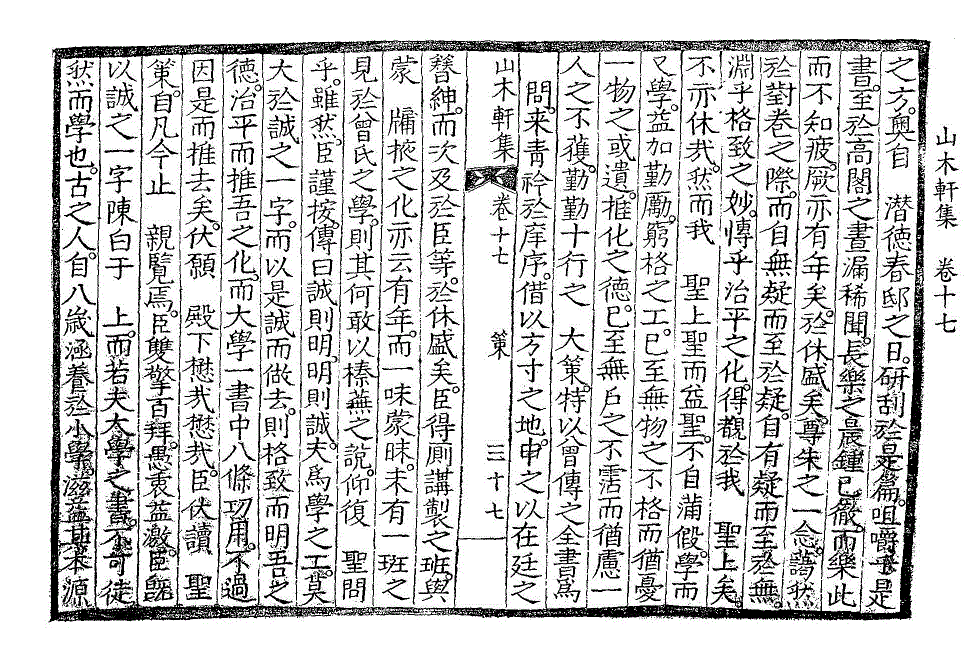 之方。奥自 潜德春邸之日。研刮于是篇。咀嚼乎是书。至于高阁之昼漏稀闻。长乐之晨钟已彻。而乐此而不知疲。厥亦有年矣。于休盛矣。尊朱之一念。蔼然于对卷之际。而自无疑而至于疑。自有疑而至于无。渊乎格致之妙。博乎治平之化。得睹于我 圣上矣。不亦休哉。然而我 圣上圣而益圣。不自满假。学而又学。益加勤励。穷格之工。已至无物之不格而犹忧一物之或遗。推化之德。已至无户之不沾而犹虑一人之不获。勤勤十行之 大策。特以曾传之全书为 问。来青衿于庠序。借以方寸之地。申之以在廷之簪绅。而次及于臣等。于休盛矣。臣得厕讲制之班。与蒙 牖掖之化亦云有年。而一味蒙昧。未有一斑之见于曾氏之学。则其何敢以榛芜之说。仰复 圣问乎。虽然。臣谨按。传曰诚则明。明则诚。夫为学之工。莫大于诚之一字。而以是诚而做去。则格致而明吾之德。治平而推吾之化。而大学一书中八条功用。不过因是而推去矣。伏愿 殿下懋哉懋哉。臣伏读 圣策。自凡今止 亲览焉。臣双擎百拜。愚衷益激。臣既以诚之一字陈白于 上。而若夫大学之书。不可徒然而学也。古之人。自八岁涵养于小学。滋益其本源
之方。奥自 潜德春邸之日。研刮于是篇。咀嚼乎是书。至于高阁之昼漏稀闻。长乐之晨钟已彻。而乐此而不知疲。厥亦有年矣。于休盛矣。尊朱之一念。蔼然于对卷之际。而自无疑而至于疑。自有疑而至于无。渊乎格致之妙。博乎治平之化。得睹于我 圣上矣。不亦休哉。然而我 圣上圣而益圣。不自满假。学而又学。益加勤励。穷格之工。已至无物之不格而犹忧一物之或遗。推化之德。已至无户之不沾而犹虑一人之不获。勤勤十行之 大策。特以曾传之全书为 问。来青衿于庠序。借以方寸之地。申之以在廷之簪绅。而次及于臣等。于休盛矣。臣得厕讲制之班。与蒙 牖掖之化亦云有年。而一味蒙昧。未有一斑之见于曾氏之学。则其何敢以榛芜之说。仰复 圣问乎。虽然。臣谨按。传曰诚则明。明则诚。夫为学之工。莫大于诚之一字。而以是诚而做去。则格致而明吾之德。治平而推吾之化。而大学一书中八条功用。不过因是而推去矣。伏愿 殿下懋哉懋哉。臣伏读 圣策。自凡今止 亲览焉。臣双擎百拜。愚衷益激。臣既以诚之一字陈白于 上。而若夫大学之书。不可徒然而学也。古之人。自八岁涵养于小学。滋益其本源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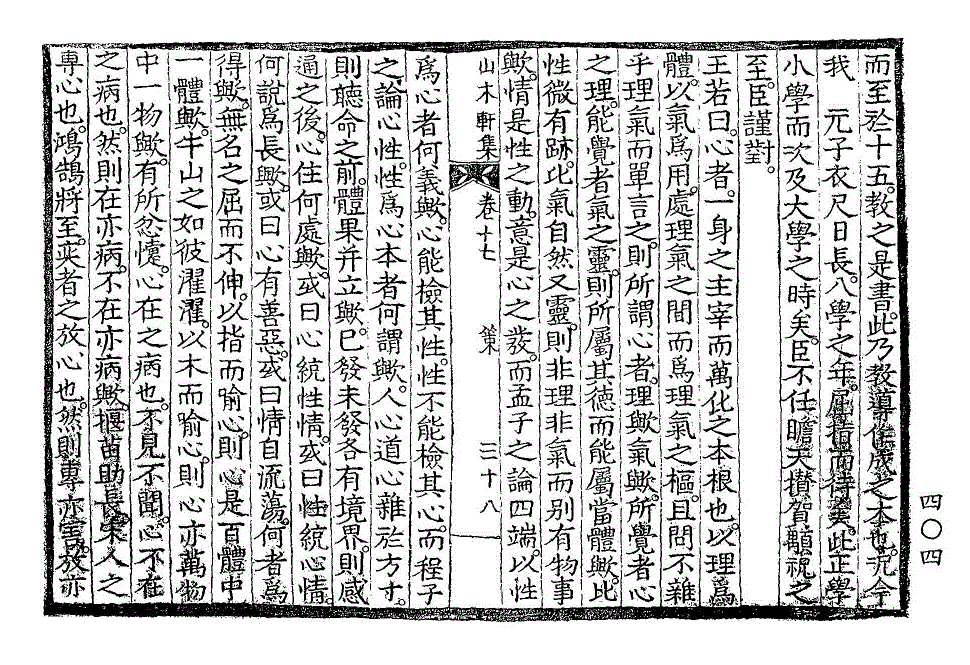 而至于十五。教之是书。此乃教导作成之本也。况今我 元子衣尺日长。入学之年。屈指而待矣。此正学小学而次及大学之时矣。臣不任瞻天攒贺颙祝之至。臣谨对。
而至于十五。教之是书。此乃教导作成之本也。况今我 元子衣尺日长。入学之年。屈指而待矣。此正学小学而次及大学之时矣。臣不任瞻天攒贺颙祝之至。臣谨对。[心说]
王若曰。心者。一身之主宰而万化之本根也。以理为体。以气为用。处理气之间而为理气之枢。且问不杂乎理气而单言之。则所谓心者。理欤气欤。所觉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则所属其德而能属当体欤。比性微有迹。比气自然又灵。则非理非气而别有物事欤。情是性之动。意是心之发。而孟子之论四端。以性为心者何义欤。心能检其性。性不能检其心。而程子之论心性。性为心本者何谓欤。人心道心杂于方寸。则听命之前。体果并立欤。已发未发各有境界。则感通之后。心住何处欤。或曰心统性情。或曰性统心情。何说为长欤。或曰心有善恶。或曰情自流荡。何者为得欤。无名之屈而不伸。以指而喻心。则心是百体中一体欤。牛山之如彼濯濯。以木而喻心。则心亦万物中一物欤。有所忿懥。心在之病也。不见不闻。心不在之病也。然则在亦病。不在亦病欤。揠苗助长。宋人之专心也。鸿鹄将至。奕者之放心也。然则专亦害。放亦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5H 页
 害欤。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此心之活机如画。心存诚敬。不如无心。樵夫之一言足听。皆可辨其得失欤。发者方往。未发者方来。中和之旧说也。思虑未萌。知觉不昧。后来之定论也。亦可论其指归欤。天地无心。而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草木无心。而记曰如松柏之有心。既无血气之郛郭。则神明安所舍欤。天下之心。各殊愿欲。而大学曰絜矩。圣凡之心。奚啻霄壤。而论语曰忠恕。既有好恶之同异。则推及安所施欤。天光云影。何等心法欤。光风霁月。何如胸次欤。浮念客虑。何起而何灭欤。蓬心宿物。孰诱而孰夺欤。良知良能。赤子之心。而大人之不失者。可指其实欤。三月不违。颜氏之心。而一间之未达者。可觑其隙欤。吾儒以虚灵为心。佛氏以知觉为心。道家以魂魄为心。一心也而见有三层欤。一方寸也而心有三种欤。如游骑之太远。如主翁之出他。则此时神舍有谁主张。所以宰物而反宰于物。所以役形而反役于形。则此时天君属谁句当欤。大抵心之为物。敛之不盈。充之无穷。尧舜之授受此心。圣贤之教学此心。一事一物之应接亦此心。大本大经之弥纶亦此心。而自精一执中以下。治心之诀。率皆就发处言之。盖心是活物必待其
害欤。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此心之活机如画。心存诚敬。不如无心。樵夫之一言足听。皆可辨其得失欤。发者方往。未发者方来。中和之旧说也。思虑未萌。知觉不昧。后来之定论也。亦可论其指归欤。天地无心。而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草木无心。而记曰如松柏之有心。既无血气之郛郭。则神明安所舍欤。天下之心。各殊愿欲。而大学曰絜矩。圣凡之心。奚啻霄壤。而论语曰忠恕。既有好恶之同异。则推及安所施欤。天光云影。何等心法欤。光风霁月。何如胸次欤。浮念客虑。何起而何灭欤。蓬心宿物。孰诱而孰夺欤。良知良能。赤子之心。而大人之不失者。可指其实欤。三月不违。颜氏之心。而一间之未达者。可觑其隙欤。吾儒以虚灵为心。佛氏以知觉为心。道家以魂魄为心。一心也而见有三层欤。一方寸也而心有三种欤。如游骑之太远。如主翁之出他。则此时神舍有谁主张。所以宰物而反宰于物。所以役形而反役于形。则此时天君属谁句当欤。大抵心之为物。敛之不盈。充之无穷。尧舜之授受此心。圣贤之教学此心。一事一物之应接亦此心。大本大经之弥纶亦此心。而自精一执中以下。治心之诀。率皆就发处言之。盖心是活物必待其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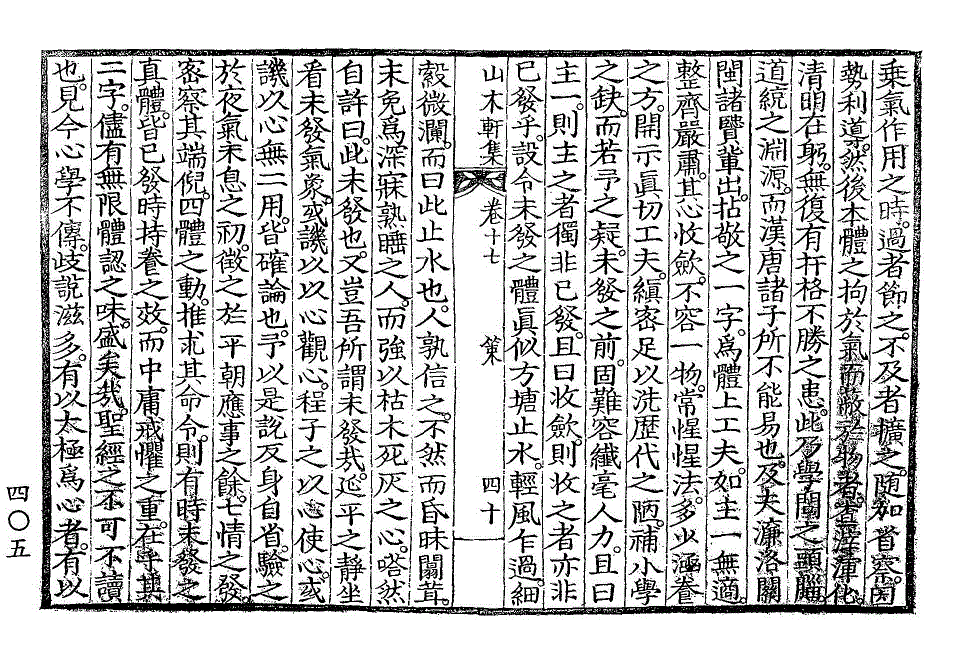 乘气作用之时。过者节之。不及者扩之。随加省察。因势利导。然后本体之拘于气而蔽于物者。查滓浑化。清明在躬。无复有捍格不胜之患。此乃学问之头脑。道统之渊源。而汉唐诸子所不能易也。及夫濂洛关闽诸贤辈出。拈敬之一字。为体上工夫。如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常惺惺法。多少涵养之方。开示真切工夫。缜密足以洗历代之陋。补小学之缺。而若予之疑。未发之前。固难容纤毫人力。且曰主一。则主之者独非已发。且曰收敛。则收之者亦非已发乎。设令未发之体真似方塘止水。轻风乍过。细縠微澜。而曰此止水也。人孰信之。不然而昏昧阘茸。未免为深寐熟睡之人。而强以枯木死灰之心。嗒然自许曰。此未发也。又岂吾所谓未发哉。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象。或讥以以心观心。程子之以心使心。或讥以心无二用。皆确论也。予以是说反身自省。验之于夜气未息之初。徵之于平朝应事之馀。七情之发。密察其端倪。四体之动。推求其命令。则有时未发之真体。皆已发时持养之效。而中庸戒惧之重。在乎其二字。尽有无限体认之味。盛矣哉。圣经之不可不读也。见今心学不传。歧说滋多。有以太极为心者。有以
乘气作用之时。过者节之。不及者扩之。随加省察。因势利导。然后本体之拘于气而蔽于物者。查滓浑化。清明在躬。无复有捍格不胜之患。此乃学问之头脑。道统之渊源。而汉唐诸子所不能易也。及夫濂洛关闽诸贤辈出。拈敬之一字。为体上工夫。如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常惺惺法。多少涵养之方。开示真切工夫。缜密足以洗历代之陋。补小学之缺。而若予之疑。未发之前。固难容纤毫人力。且曰主一。则主之者独非已发。且曰收敛。则收之者亦非已发乎。设令未发之体真似方塘止水。轻风乍过。细縠微澜。而曰此止水也。人孰信之。不然而昏昧阘茸。未免为深寐熟睡之人。而强以枯木死灰之心。嗒然自许曰。此未发也。又岂吾所谓未发哉。延平之静坐看未发气象。或讥以以心观心。程子之以心使心。或讥以心无二用。皆确论也。予以是说反身自省。验之于夜气未息之初。徵之于平朝应事之馀。七情之发。密察其端倪。四体之动。推求其命令。则有时未发之真体。皆已发时持养之效。而中庸戒惧之重。在乎其二字。尽有无限体认之味。盛矣哉。圣经之不可不读也。见今心学不传。歧说滋多。有以太极为心者。有以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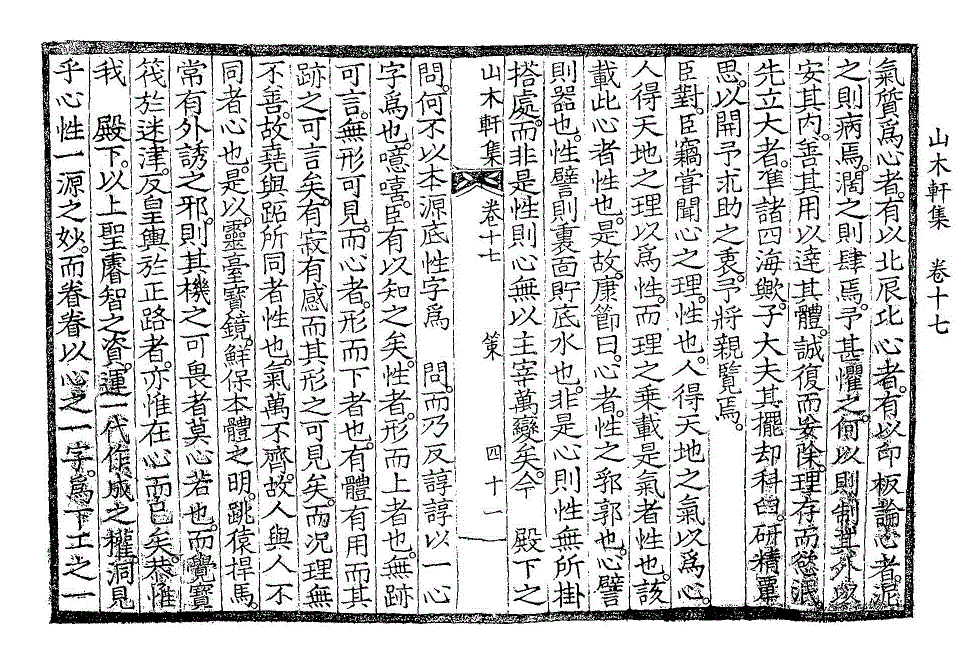 气质为心者。有以北辰比心者。有以印板论心者。泥之则病焉。阔之则肆焉。予甚惧之。何以则制其外以安其内。善其用以达其体。诚复而妄除。理存而欲泯。先立大者。准诸四海欤。子大夫其摆却科臼。研精覃思。以开予求助之衷。予将亲览焉。
气质为心者。有以北辰比心者。有以印板论心者。泥之则病焉。阔之则肆焉。予甚惧之。何以则制其外以安其内。善其用以达其体。诚复而妄除。理存而欲泯。先立大者。准诸四海欤。子大夫其摆却科臼。研精覃思。以开予求助之衷。予将亲览焉。臣对。臣窃尝闻心之理。性也。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心。人得天地之理以为性。而理之乘载是气者性也。该载此心者性也。是故。康节曰。心者。性之郛郭也。心譬则器也。性譬则里面贮底水也。非是心则性无所挂搭处。而非是性则心无以主宰万变矣。今 殿下之问。何不以本源底性字为 问。而乃反谆谆以一心字为也。噫嘻。臣有以知之矣。性者。形而上者也。无迹可言。无形可见。而心者。形而下者也。有体有用而其迹之可言矣。有寂有感而其形之可见矣。而况理无不善。故尧与蹠所同者性也。气万不齐。故人与人不同者心也。是以。灵台宝镜。鲜保本体之明。跳猿捍马。常有外诱之邪。则其机之可畏者莫心若也。而觉宝筏于迷津。反皇舆于正路者。亦惟在心而已矣。恭惟我 殿下。以上圣睿智之资。运一代作成之权。洞见乎心性一源之妙。而眷眷以心之一字。为下工之一
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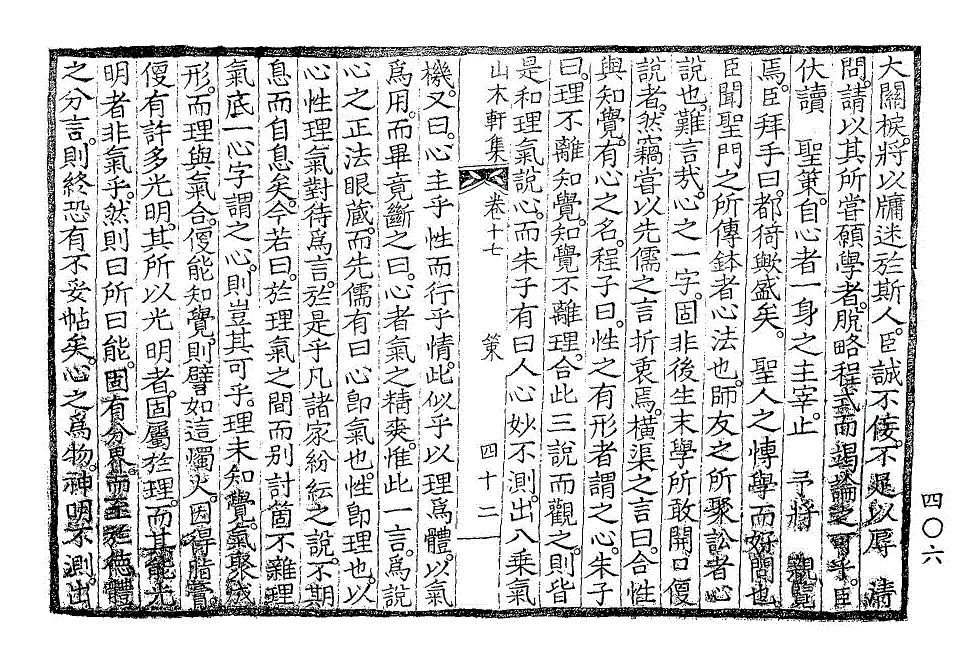 大关棙。将以牗迷于斯人。臣诚不佞。不足以辱 清问。请以其所尝愿学者。脱略程式而竭论之可乎。臣伏读 圣策。自心者一身之主宰。止 予将 亲览焉。臣拜手曰。都猗欤盛矣。 圣人之博学而好问也。臣闻圣门之所传钵者心法也。师友之所聚讼者心说也。难言哉。心之一字。固非后生末学所敢开口便说者。然窃尝以先儒之言折衷焉。横渠之言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程子曰。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朱子曰。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合此三说而观之。则皆是和理气说心。而朱子有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又曰。心主乎性而行乎情。此似乎以理为体。以气为用。而毕竟断之曰。心者气之精爽。惟此一言。为说心之正法眼藏。而先儒有曰心即气也。性即理也。以心性理气对待为言。于是乎凡诸家纷纭之说。不期息而自息矣。今若曰。于理气之间而别讨个不杂理气底一心字谓之心。则岂其可乎。理未知觉。气聚成形。而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则譬如这烛火。因得脂膏。便有许多光明。其所以光明者。固属于理。而其能光明者非气乎。然则曰所曰能。固有分界。而至于德体之分言。则终恐有不妥帖矣。心之为物。神明不测。出
大关棙。将以牗迷于斯人。臣诚不佞。不足以辱 清问。请以其所尝愿学者。脱略程式而竭论之可乎。臣伏读 圣策。自心者一身之主宰。止 予将 亲览焉。臣拜手曰。都猗欤盛矣。 圣人之博学而好问也。臣闻圣门之所传钵者心法也。师友之所聚讼者心说也。难言哉。心之一字。固非后生末学所敢开口便说者。然窃尝以先儒之言折衷焉。横渠之言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程子曰。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朱子曰。理不离知觉。知觉不离理。合此三说而观之。则皆是和理气说心。而朱子有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又曰。心主乎性而行乎情。此似乎以理为体。以气为用。而毕竟断之曰。心者气之精爽。惟此一言。为说心之正法眼藏。而先儒有曰心即气也。性即理也。以心性理气对待为言。于是乎凡诸家纷纭之说。不期息而自息矣。今若曰。于理气之间而别讨个不杂理气底一心字谓之心。则岂其可乎。理未知觉。气聚成形。而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则譬如这烛火。因得脂膏。便有许多光明。其所以光明者。固属于理。而其能光明者非气乎。然则曰所曰能。固有分界。而至于德体之分言。则终恐有不妥帖矣。心之为物。神明不测。出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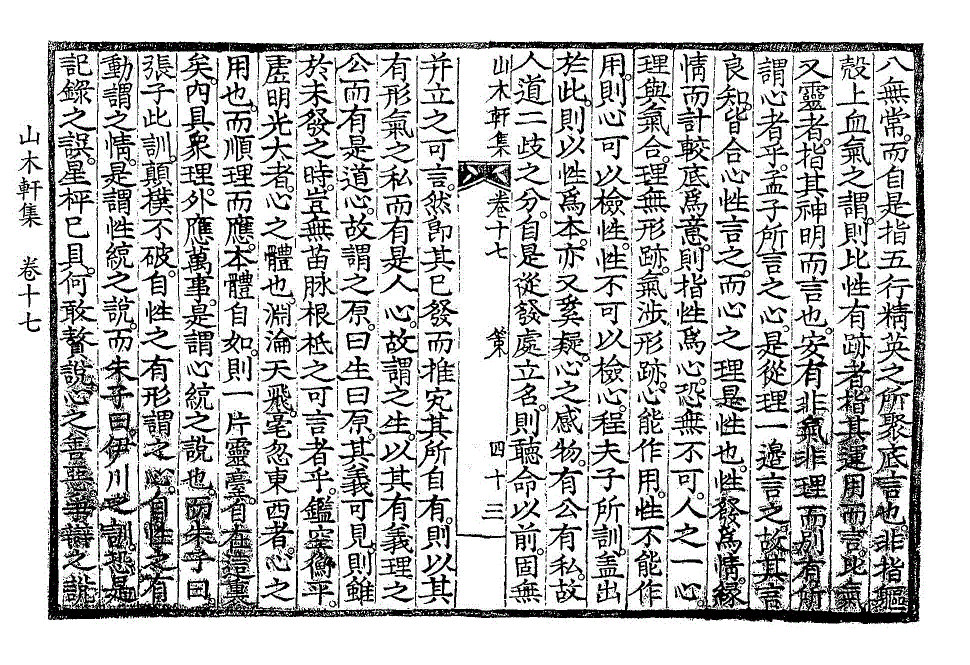 入无常。而自是指五行精英之所聚底言也。非指躯壳上血气之谓。则比性有迹者。指其运用而言。比气又灵者。指其神明而言也。安有非气非理而别有所谓心者乎。孟子所言之心。是从理一边言之。故其言良知。皆合心性言之。而心之理是性也。性发为情。缘情而计较底为意。则指性为心。恐无不可。人之一心。理与气合。理无形迹。气涉形迹。心能作用。性不能作用。则心可以检性。性不可以检心。程夫子所训。盖出于此。则以性为本。亦又奚疑。心之感物。有公有私。故人道二歧之分。自是从发处立名。则听命以前。固无并立之可言。然即其已发而推宄其所自有。则以其有形气之私而有是人心。故谓之生。以其有义理之公而有是道心。故谓之原。曰生曰原。其义可见。则虽于未发之时。岂无苗脉根柢之可言者乎。鉴空衡平。虚明光大者。心之体也。渊沦天飞。毫忽东西者。心之用也。而顺理而应。本体自如。则一片灵台。自在这里矣。内具众理。外应万事。是谓心统之说也。而朱子曰。张子此训。颠扑不破。自性之有形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谓之情。是谓性统之说。而朱子曰。伊川之训。恐是记录之误。星枰已具。何敢赘说。心之善恶。争辩之说
入无常。而自是指五行精英之所聚底言也。非指躯壳上血气之谓。则比性有迹者。指其运用而言。比气又灵者。指其神明而言也。安有非气非理而别有所谓心者乎。孟子所言之心。是从理一边言之。故其言良知。皆合心性言之。而心之理是性也。性发为情。缘情而计较底为意。则指性为心。恐无不可。人之一心。理与气合。理无形迹。气涉形迹。心能作用。性不能作用。则心可以检性。性不可以检心。程夫子所训。盖出于此。则以性为本。亦又奚疑。心之感物。有公有私。故人道二歧之分。自是从发处立名。则听命以前。固无并立之可言。然即其已发而推宄其所自有。则以其有形气之私而有是人心。故谓之生。以其有义理之公而有是道心。故谓之原。曰生曰原。其义可见。则虽于未发之时。岂无苗脉根柢之可言者乎。鉴空衡平。虚明光大者。心之体也。渊沦天飞。毫忽东西者。心之用也。而顺理而应。本体自如。则一片灵台。自在这里矣。内具众理。外应万事。是谓心统之说也。而朱子曰。张子此训。颠扑不破。自性之有形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谓之情。是谓性统之说。而朱子曰。伊川之训。恐是记录之误。星枰已具。何敢赘说。心之善恶。争辩之说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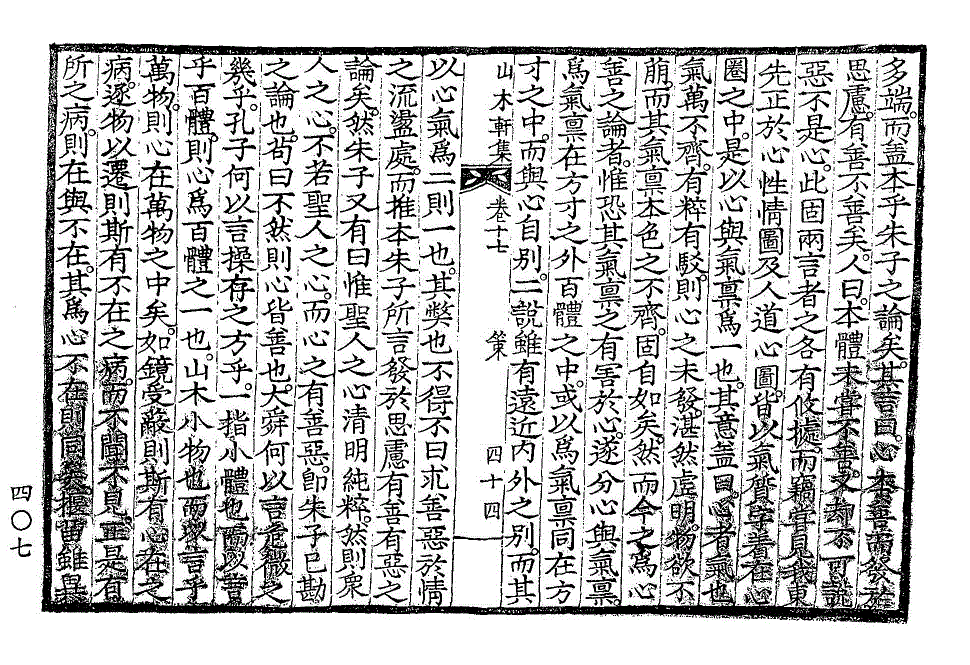 多端。而盖本乎朱子之论矣。其言曰。心本善而发于思虑。有善不善矣。人曰。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不是心。此固两言者之各有攸据。而窃尝见我东先正于心性情图及人道心图。皆以气质字着在心圈之中。是以心与气禀为一也。其意盖曰。心者气也。气万不齐。有粹有驳。则心之未发。湛然虚明。物欲不萌。而其气禀本色之不齐。固自如矣。然而今之为心善之论者。惟恐其气禀之有害于心。遂分心与气禀。为气禀在方寸之外百体之中。或以为气禀同在方寸之中。而与心自别。二说虽有远近内外之别。而其以心气为二则一也。其弊也不得不曰求善恶于情之流荡处。而推本朱子所言发于思虑有善有恶之论矣。然朱子又有曰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然则众人之心。不若圣人之心。而心之有善恶。即朱子已勘之论也。苟曰不然则心皆善也。大舜何以言危微之几乎。孔子何以言操存之方乎。一指小体也而以言乎百体。则心为百体之一也。山木小物也而以言乎万物。则心在万物之中矣。如镜受蔽则斯有心在之病。逐物以迁则斯有不在之病。而不闻不见。正是有所之病。则在与不在。其为心不在则同矣。揠苗虽异
多端。而盖本乎朱子之论矣。其言曰。心本善而发于思虑。有善不善矣。人曰。本体未尝不善。又却不可说恶不是心。此固两言者之各有攸据。而窃尝见我东先正于心性情图及人道心图。皆以气质字着在心圈之中。是以心与气禀为一也。其意盖曰。心者气也。气万不齐。有粹有驳。则心之未发。湛然虚明。物欲不萌。而其气禀本色之不齐。固自如矣。然而今之为心善之论者。惟恐其气禀之有害于心。遂分心与气禀。为气禀在方寸之外百体之中。或以为气禀同在方寸之中。而与心自别。二说虽有远近内外之别。而其以心气为二则一也。其弊也不得不曰求善恶于情之流荡处。而推本朱子所言发于思虑有善有恶之论矣。然朱子又有曰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然则众人之心。不若圣人之心。而心之有善恶。即朱子已勘之论也。苟曰不然则心皆善也。大舜何以言危微之几乎。孔子何以言操存之方乎。一指小体也而以言乎百体。则心为百体之一也。山木小物也而以言乎万物。则心在万物之中矣。如镜受蔽则斯有心在之病。逐物以迁则斯有不在之病。而不闻不见。正是有所之病。则在与不在。其为心不在则同矣。揠苗虽异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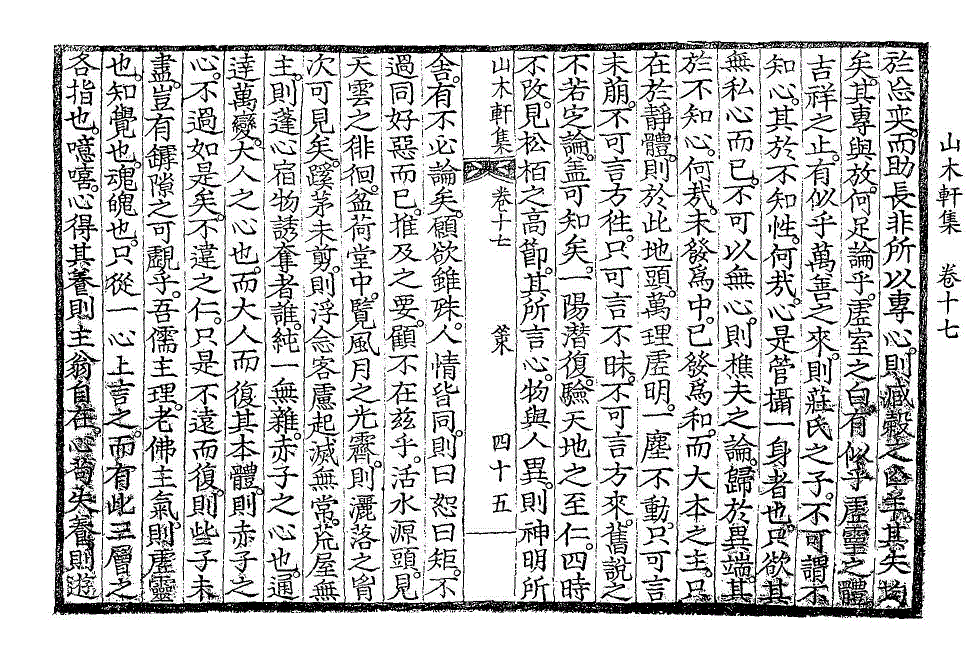 于忘奕。而助长非所以专心。则臧谷之亡羊。其失均矣。其专与放。何足论乎。虚室之白。有似乎虚灵之体吉祥之止。有似乎万善之来。则庄氏之子。不可谓不知心。其于不知性。何哉。心是管摄一身者也。只欲其无私心而已。不可以无心。则樵夫之论。归于异端。其于不知心。何哉。未发为中。已发为和。而大本之主。只在于静体。则于此地头。万理虚明。一尘不动。只可言未萌。不可言方往。只可言不昧。不可言方来。旧说之不若定论。盖可知矣。一阳潜复。验天地之至仁。四时不改。见松柏之高节。其所言心。物与人异。则神明所舍。有不必论矣。愿欲虽殊。人情皆同。则曰恕曰矩。不过同好恶而已。推及之要。顾不在玆乎。活水源头。见天云之徘徊。盆荷堂中。览风月之光霁。则洒落之胸次可见矣。蹊茅未剪。则浮念客虑起灭无常。荒屋无主。则蓬心宿物诱夺者谁。纯一无杂。赤子之心也。通达万变。大人之心也。而大人而复其本体。则赤子之心。不过如是矣。不违之仁。只是不远而复。则些子未尽。岂有罅隙之可觑乎。吾儒主理。老佛主气。则虚灵也。知觉也。魂魄也。只从一心上言之。而有此三层之各指也。噫嘻。心得其养则主翁自在。心苟失养则游
于忘奕。而助长非所以专心。则臧谷之亡羊。其失均矣。其专与放。何足论乎。虚室之白。有似乎虚灵之体吉祥之止。有似乎万善之来。则庄氏之子。不可谓不知心。其于不知性。何哉。心是管摄一身者也。只欲其无私心而已。不可以无心。则樵夫之论。归于异端。其于不知心。何哉。未发为中。已发为和。而大本之主。只在于静体。则于此地头。万理虚明。一尘不动。只可言未萌。不可言方往。只可言不昧。不可言方来。旧说之不若定论。盖可知矣。一阳潜复。验天地之至仁。四时不改。见松柏之高节。其所言心。物与人异。则神明所舍。有不必论矣。愿欲虽殊。人情皆同。则曰恕曰矩。不过同好恶而已。推及之要。顾不在玆乎。活水源头。见天云之徘徊。盆荷堂中。览风月之光霁。则洒落之胸次可见矣。蹊茅未剪。则浮念客虑起灭无常。荒屋无主。则蓬心宿物诱夺者谁。纯一无杂。赤子之心也。通达万变。大人之心也。而大人而复其本体。则赤子之心。不过如是矣。不违之仁。只是不远而复。则些子未尽。岂有罅隙之可觑乎。吾儒主理。老佛主气。则虚灵也。知觉也。魂魄也。只从一心上言之。而有此三层之各指也。噫嘻。心得其养则主翁自在。心苟失养则游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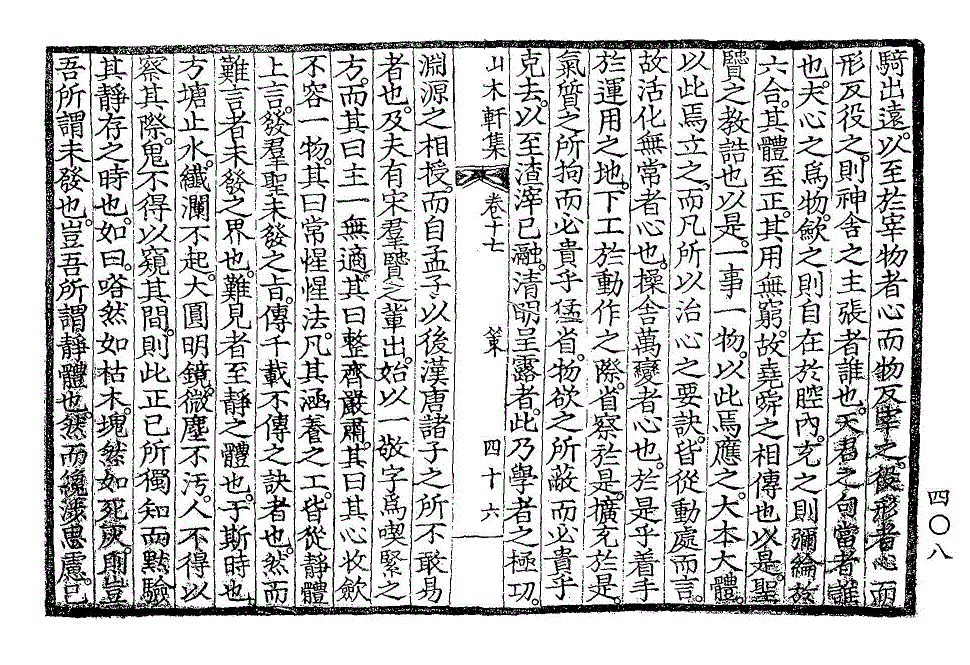 骑出远。以至于宰物者心而物反宰之。役形者心而形反役之。则神舍之主张者谁也。天君之句当者谁也。夫心之为物。敛之则自在于腔内。充之则弥纶于六合。其体至正。其用无穷。故尧舜之相传也以是。圣贤之教诰也以是。一事一物。以此焉应之。大本大体。以此焉立之。而凡所以治心之要诀。皆从动处而言。故活化无常者心也。操舍万变者心也。于是乎着手于运用之地。下工于动作之际。省察于是。扩充于是。气质之所拘而必贵乎猛省。物欲之所蔽而必贵乎克去。以至渣滓已融。清明呈露者。此乃学者之极功。渊源之相授。而自孟子以后汉唐诸子之所不敢易者也。及夫有宋群贤之辈出。始以一敬字为吃紧之方。而其曰主一无适。其曰整齐严肃。其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其曰常惺惺法。凡其涵养之工。皆从静体上言。发群圣未发之旨。传千载不传之诀者也。然而难言者未发之界也。难见者至静之体也。于斯时也。方塘止水。纤澜不起。大圆明镜。微尘不污。人不得以察其际。鬼不得以窥其间。则此正己所独知而默验其静存之时也。如曰。嗒然如枯木。块然如死灰。则岂吾所谓未发也。岂吾所谓静体也。然而才涉思虑。已
骑出远。以至于宰物者心而物反宰之。役形者心而形反役之。则神舍之主张者谁也。天君之句当者谁也。夫心之为物。敛之则自在于腔内。充之则弥纶于六合。其体至正。其用无穷。故尧舜之相传也以是。圣贤之教诰也以是。一事一物。以此焉应之。大本大体。以此焉立之。而凡所以治心之要诀。皆从动处而言。故活化无常者心也。操舍万变者心也。于是乎着手于运用之地。下工于动作之际。省察于是。扩充于是。气质之所拘而必贵乎猛省。物欲之所蔽而必贵乎克去。以至渣滓已融。清明呈露者。此乃学者之极功。渊源之相授。而自孟子以后汉唐诸子之所不敢易者也。及夫有宋群贤之辈出。始以一敬字为吃紧之方。而其曰主一无适。其曰整齐严肃。其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其曰常惺惺法。凡其涵养之工。皆从静体上言。发群圣未发之旨。传千载不传之诀者也。然而难言者未发之界也。难见者至静之体也。于斯时也。方塘止水。纤澜不起。大圆明镜。微尘不污。人不得以察其际。鬼不得以窥其间。则此正己所独知而默验其静存之时也。如曰。嗒然如枯木。块然如死灰。则岂吾所谓未发也。岂吾所谓静体也。然而才涉思虑。已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9H 页
 是动处。则其曰主一。而主之者非所谓已发乎。其曰收敛。而收之者非所谓动处乎。静坐看未发。周子之论不几乎以心观心之讥乎。以心使心。程子之训不几于心无二用之科乎。此我 圣上所以默察于夜气清明之时。细玩乎平朝应务之际。而验端倪于七情之方发。推命令于四体之运用。深有契乎思传戒惧之工。重在于乎其二字之上。用工于静存之体。而收效于动察之时。猗欤盛矣。深造之工。有得于孔训。独觉之妙。潜孚乎程说。若是乎圣经之不可以不读也。奈之何 明圣之工日勤于上。而下无辈出之贤。心学之不传已久。歧贰之论说愈多。有单指太极而为心者。有专指气质而为心者。北辰之比也。印板之论也。不胜其纷纭。此 圣上所以瞿然而却顾。渊然而兴思。思所以制外而安内。善用而达体。发 问于策士之庭。又进臣等而谆谆然 问之者也。呜呼。臣愚颛蒙。顾何以仰塞 明问之万一乎。虽然。臣尝闻心体之不明。由于择术之不精。择术之不精。由于师道之不尊。凡今之悠悠万弊。职由此起矣。诚使一世之章甫。读书则深究乎择术之工。讲学则着力于尊师之道。则其所谓择术者。即所以操存涵养之方也。
是动处。则其曰主一。而主之者非所谓已发乎。其曰收敛。而收之者非所谓动处乎。静坐看未发。周子之论不几乎以心观心之讥乎。以心使心。程子之训不几于心无二用之科乎。此我 圣上所以默察于夜气清明之时。细玩乎平朝应务之际。而验端倪于七情之方发。推命令于四体之运用。深有契乎思传戒惧之工。重在于乎其二字之上。用工于静存之体。而收效于动察之时。猗欤盛矣。深造之工。有得于孔训。独觉之妙。潜孚乎程说。若是乎圣经之不可以不读也。奈之何 明圣之工日勤于上。而下无辈出之贤。心学之不传已久。歧贰之论说愈多。有单指太极而为心者。有专指气质而为心者。北辰之比也。印板之论也。不胜其纷纭。此 圣上所以瞿然而却顾。渊然而兴思。思所以制外而安内。善用而达体。发 问于策士之庭。又进臣等而谆谆然 问之者也。呜呼。臣愚颛蒙。顾何以仰塞 明问之万一乎。虽然。臣尝闻心体之不明。由于择术之不精。择术之不精。由于师道之不尊。凡今之悠悠万弊。职由此起矣。诚使一世之章甫。读书则深究乎择术之工。讲学则着力于尊师之道。则其所谓择术者。即所以操存涵养之方也。山木轩集卷之十七○应制录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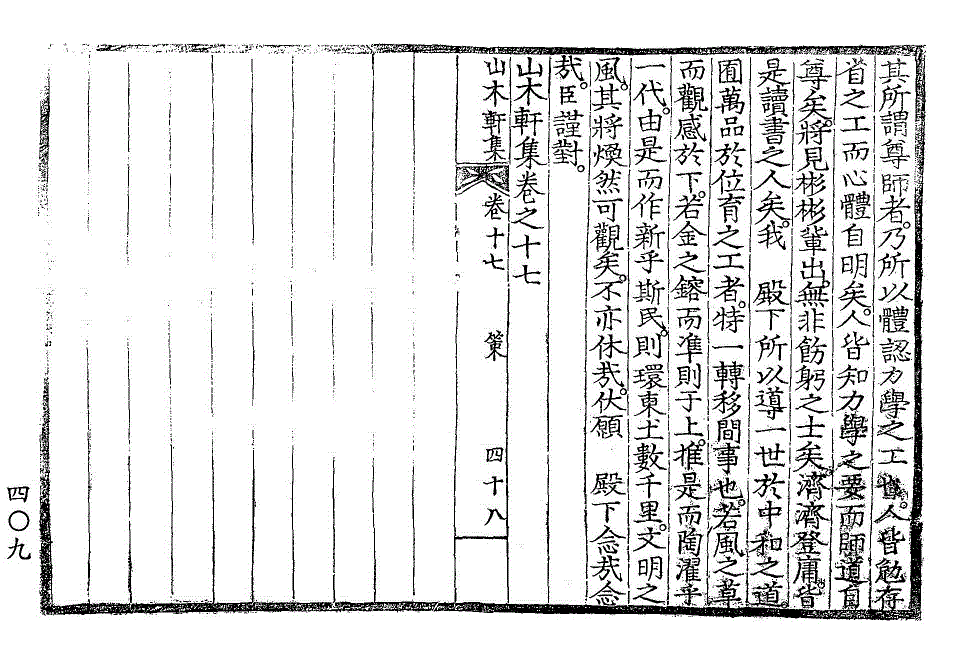 其所谓尊师者。乃所以体认力学之工也。人皆勉存省之工而心体自明矣。人皆知力学之要而师道自尊矣。将见彬彬辈出。无非饬躬之士矣。济济登庸。皆是读书之人矣。我 殿下所以导一世于中和之道。囿万品于位育之工者。特一转移间事也。若风之草而观感于下。若金之镕而准则于上。推是而陶濯乎一代。由是而作新乎斯民。则环东土数千里。文明之风。其将焕然可观矣。不亦休哉。伏愿 殿下念哉念哉。臣谨对。
其所谓尊师者。乃所以体认力学之工也。人皆勉存省之工而心体自明矣。人皆知力学之要而师道自尊矣。将见彬彬辈出。无非饬躬之士矣。济济登庸。皆是读书之人矣。我 殿下所以导一世于中和之道。囿万品于位育之工者。特一转移间事也。若风之草而观感于下。若金之镕而准则于上。推是而陶濯乎一代。由是而作新乎斯民。则环东土数千里。文明之风。其将焕然可观矣。不亦休哉。伏愿 殿下念哉念哉。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