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x 页
山木轩集卷之六
讲义
讲义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6H 页
 小雅
小雅御制条问曰。雅有大小正变。大小之殊。是周公所定则固可信也。正变之异。非孔子所言。故或甚疑之。未知如何。
臣对曰。诗是匹夫匹妇胸中全经。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善恶邪正之分。此风雅之音自有正变之异。而以其性情上邪正善恶。辨其政事中兴废盛衰。则比雅有大小。便有正变。而出于其情之善且正而其政之盛且兴者为正雅。出于其情之恶且邪而其政之废且衰者为变雅。苟不先明乎正变之音。则无以知其性情善恶之分而劝惩之耳。此千古说诗之要旨。而三百篇之头颅也。正变二字。虽非孔子之所言。而雅颂各得其所者。是谓其善恶邪正之以类各排也。正变之意。于此盖可见。而朱子有曰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则臣何敢臆对欤。
御制条问曰。雅者。正也。变雅之名。是变中之正耶。是正中之变耶。孔氏曰。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变者。谓之变小雅。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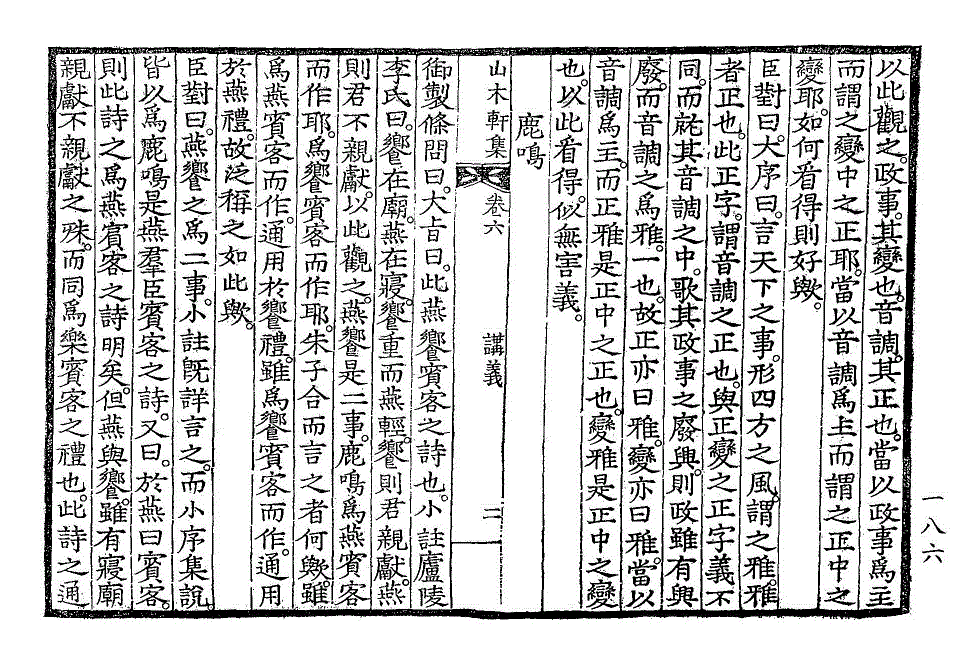 以此观之。政事。其变也。音调。其正也。当以政事为主而谓之变中之正耶。当以音调为主而谓之正中之变耶。如何看得则好欤。
以此观之。政事。其变也。音调。其正也。当以政事为主而谓之变中之正耶。当以音调为主而谓之正中之变耶。如何看得则好欤。臣对曰。大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此正字。谓音调之正也。与正变之正字义不同。而就其音调之中。歌其政事之废兴。则政虽有兴废。而音调之为雅。一也。故正亦曰雅。变亦曰雅。当以音调为主。而正雅是正中之正也。变雅是正中之变也。以此看得。似无害义。
鹿鸣
御制条问曰。大旨曰。此燕飨宾客之诗也。小注庐陵李氏曰。飨在庙。燕在寝。飨重而燕轻。飨则君亲献。燕则君不亲献。以此观之。燕飨是二事。鹿鸣为燕宾客而作耶。为飨宾客而作耶。朱子合而言之者何欤。虽为燕宾客而作。通用于飨礼。虽为飨宾客而作。通用于燕礼。故泛称之如此欤。
臣对曰。燕飨之为二事。小注既详言之。而小序集说。皆以为鹿鸣是燕群臣宾客之诗。又曰。于燕曰宾客。则此诗之为燕宾客之诗明矣。但燕与飨。虽有寝庙亲献不亲献之殊。而同为乐宾客之礼也。此诗之通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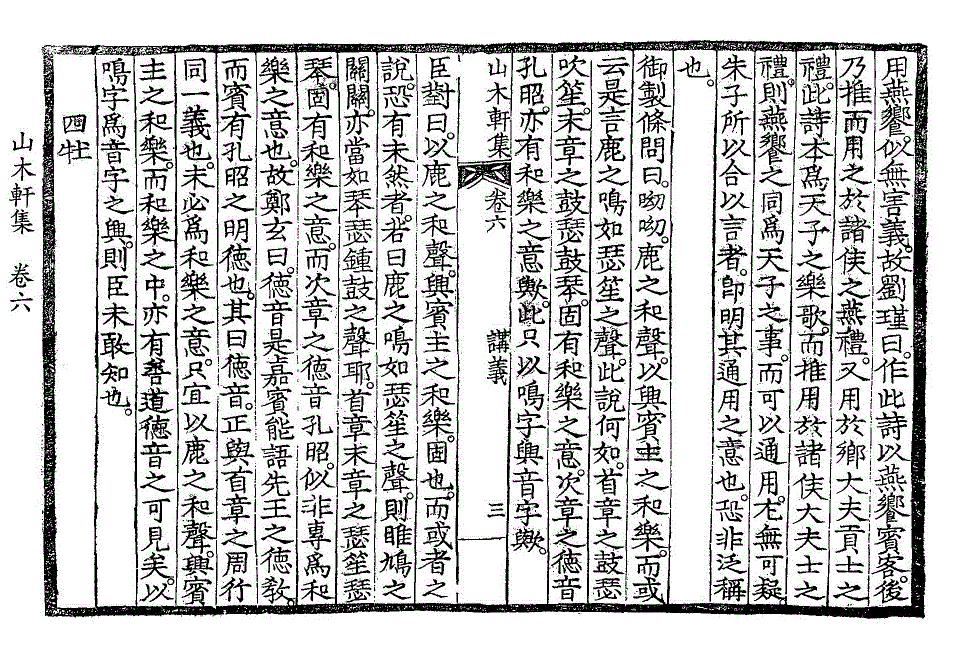 用燕飨。似无害义。故刘瑾曰。作此诗以燕飨宾客。后乃推而用之于诸侯之燕礼。又用于乡大夫贡士之礼。此诗本为天子之乐歌。而推用于诸侯大夫士之礼。则燕飨之同为天子之事。而可以通用。尤无可疑。朱子所以合以言者。即明其通用之意也。恐非泛称也。
用燕飨。似无害义。故刘瑾曰。作此诗以燕飨宾客。后乃推而用之于诸侯之燕礼。又用于乡大夫贡士之礼。此诗本为天子之乐歌。而推用于诸侯大夫士之礼。则燕飨之同为天子之事。而可以通用。尤无可疑。朱子所以合以言者。即明其通用之意也。恐非泛称也。御制条问曰。呦呦。鹿之和声。以兴宾主之和乐。而或云是言鹿之鸣如瑟笙之声。此说何如。首章之鼓瑟吹笙。末章之鼓瑟鼓琴。固有和乐之意。次章之德音孔昭。亦有和乐之意欤。此只以鸣字兴音字欤。
臣对曰。以鹿之和声。兴宾主之和乐。固也。而或者之说。恐有未然者。若曰鹿之鸣如瑟笙之声。则雎鸠之关关。亦当如琴瑟钟鼓之声耶。首章末章之瑟笙瑟琴。固有和乐之意。而次章之德音孔昭。似非专为和乐之意也。故郑玄曰。德音是嘉宾能语先王之德教。而宾有孔昭之明德也。其曰德音。正与首章之周行同一义也。未必为和乐之意。只宜以鹿之和声。兴宾主之和乐。而和乐之中。亦有善道德音之可见矣。以鸣字为音字之兴。则臣未敢知也。
四牡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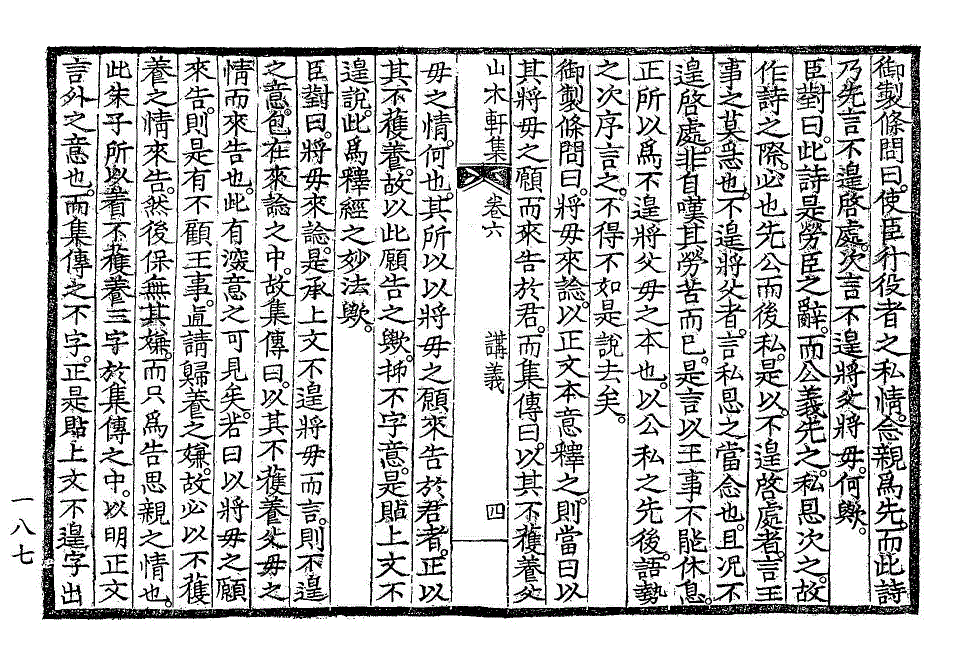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使臣行役者之私情。念亲为先。而此诗乃先言不遑启处。次言不遑将父将母。何欤。
御制条问曰。使臣行役者之私情。念亲为先。而此诗乃先言不遑启处。次言不遑将父将母。何欤。臣对曰。此诗是劳臣之辞。而公义先之。私恩次之。故作诗之际。必也先公而后私。是以。不遑启处者。言王事之莫急也。不遑将父者。言私恩之当念也。且况不遑启处。非自叹其劳苦而已。是言以王事不能休息。正所以为不遑将父母之本也。以公私之先后。语势之次序言之。不得不如是说去矣。
御制条问曰。将母来谂。以正文本意释之。则当曰以其将母之愿而来告于君。而集传曰。以其不获养父母之情。何也。其所以以将母之愿来告于君者。正以其不获养。故以此愿告之欤。抑不字意。是贴上文不遑说。此为释经之妙法欤。
臣对曰。将母来谂。是承上文不遑将母而言。则不遑之意。包在来谂之中。故集传曰。以其不获养父母之情而来告也。此有深意之可见矣。若曰以将母之愿来告。则是有不顾王事。直请归养之嫌。故必以不获养之情来告。然后保无其嫌。而只为告思亲之情也。此朱子所以着不获养三字于集传之中。以明正文言外之意也。而集传之不字。正是贴上文不遑字出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8H 页
 来也。虽谓之释经之妙法。似无不可矣。
来也。虽谓之释经之妙法。似无不可矣。皇皇者华
御制条问曰。每怀靡及。大旨以述下情为主。而兼得戒意。然春秋外传曰。君教臣曰每怀靡及云云。教是戒也。此专作戒意说。大旨与此小异。何欤。
臣对曰。皇华一章。专以述下情为主。而诗本先王敕遣使臣之语。故每怀靡及四字。亦与春秋教戒之辞同。此集传所谓因以为戒。而敕遣之际。安得无戒意乎。特以春秋是教使臣之意也。皇华是美使臣之语也。故春秋专作戒意。此诗兼得戒意。其旨之少有间然者。盖以是也。
御制条问曰。皇华与上鹿鸣。同是一时之诗。何者。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鹿鸣之示我周行。欲己之得助于贤也。皇华之周爰咨诹。欲臣之求助于贤也。其辞意如出一人之口。玆岂非其验欤。
臣对曰。鹿鸣以下五诗与天保一章。同为君燕臣臣答君之诗。则其为一时之诗。奚独皇华为然。但鹿鸣之示我周行。是人君之欲求贤以自助也。皇华之周爰咨诹。是人君欲其臣之求贤自助。而以助我也。观其语脉。似是一口气出来。则其视四牡,常棣等诗。尤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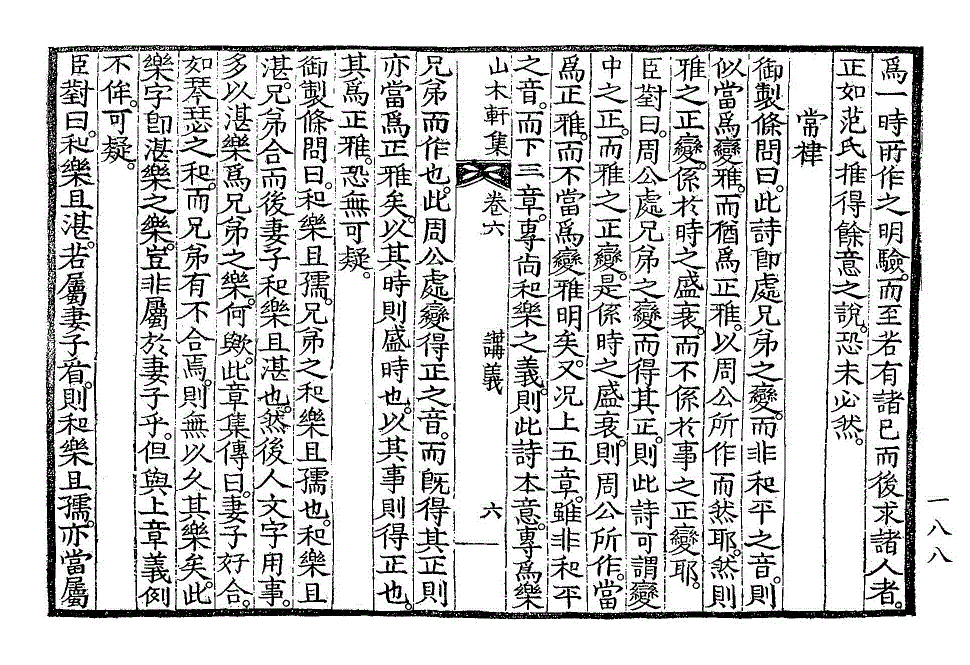 为一时所作之明验。而至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者。正如范氏推得馀意之说。恐未必然。
为一时所作之明验。而至若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者。正如范氏推得馀意之说。恐未必然。常棣
御制条问曰。此诗即处兄弟之变。而非和平之音。则似当为变雅。而犹为正雅。以周公所作而然耶。然则雅之正变。系于时之盛衰。而不系于事之正变耶。
臣对曰。周公处兄弟之变而得其正。则此诗可谓变中之正。而雅之正变。是系时之盛衰。则周公所作。当为正雅。而不当为变雅明矣。又况上五章。虽非和平之音。而下三章。专尚和乐之义。则此诗本意。专为乐兄弟而作也。此周公处变得正之音。而既得其正则亦当为正雅矣。以其时则盛时也。以其事则得正也。其为正雅。恐无可疑。
御制条问曰。和乐且孺。兄弟之和乐且孺也。和乐且湛。兄弟合而后妻子和乐且湛也。然后人文字用事。多以湛乐为兄弟之乐。何欤。此章集传曰。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则无以久其乐矣。此乐字即湛乐之乐。岂非属于妻子乎。但与上章义例不侔。可疑。
臣对曰。和乐且湛。若属妻子看。则和乐且孺。亦当属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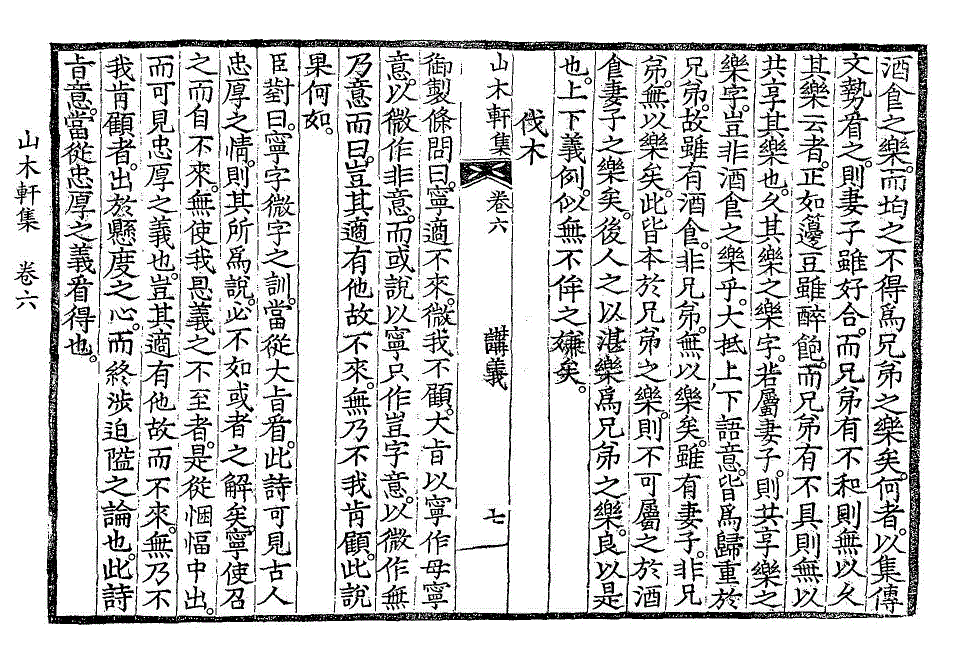 酒食之乐。而均之不得为兄弟之乐矣。何者。以集传文势看之。则妻子虽好合。而兄弟有不和则无以久其乐云者。正如笾豆虽醉饱。而兄弟有不具则无以共享其乐也。久其乐之乐字。若属妻子。则共享乐之乐字。岂非酒食之乐乎。大抵上下语意。皆为归重于兄弟。故虽有酒食。非兄弟。无以乐矣。虽有妻子。非兄弟。无以乐矣。此皆本于兄弟之乐。则不可属之于酒食妻子之乐矣。后人之以湛乐为兄弟之乐。良以是也。上下义例。似无不侔之嫌矣。
酒食之乐。而均之不得为兄弟之乐矣。何者。以集传文势看之。则妻子虽好合。而兄弟有不和则无以久其乐云者。正如笾豆虽醉饱。而兄弟有不具则无以共享其乐也。久其乐之乐字。若属妻子。则共享乐之乐字。岂非酒食之乐乎。大抵上下语意。皆为归重于兄弟。故虽有酒食。非兄弟。无以乐矣。虽有妻子。非兄弟。无以乐矣。此皆本于兄弟之乐。则不可属之于酒食妻子之乐矣。后人之以湛乐为兄弟之乐。良以是也。上下义例。似无不侔之嫌矣。伐木
御制条问曰。宁适不来。微我不顾。大旨以宁作毋宁意。以微作非意。而或说以宁只作岂字意。以微作无乃意而曰。岂其适有他故不来。无乃不我肯顾。此说果何如。
臣对曰。宁字微字之训。当从大旨看。此诗可见古人忠厚之情。则其所为说。必不如或者之解矣。宁使召之而自不来。无使我恩义之不至者。是从悃愊中出。而可见忠厚之义也。岂其适有他故而不来。无乃不我肯顾者。出于悬度之心。而终涉迫隘之论也。此诗旨意。当从忠厚之义看得也。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89L 页
 御制条问曰。民之失德。乾糇以愆。或讥其语野意薄。夫在我而言之。诚亦然矣。自他人言之。是亦人情之真切者。华元之羊羹。子公之鼋鼎。卒至于丧师乱邦。则其可惧也如是。又安可人人以君子之道责之。易需卦为饮食之象。而其下受之以讼。饮食者必有讼也。此岂非易诗人之意乎。
御制条问曰。民之失德。乾糇以愆。或讥其语野意薄。夫在我而言之。诚亦然矣。自他人言之。是亦人情之真切者。华元之羊羹。子公之鼋鼎。卒至于丧师乱邦。则其可惧也如是。又安可人人以君子之道责之。易需卦为饮食之象。而其下受之以讼。饮食者必有讼也。此岂非易诗人之意乎。臣对曰。君子之处朋友。何尝有意于饮食之厚薄。而乾糇之愆。或至失德之科。则此诗之语野意薄。或者之讥。诚亦然矣。然而饮食乃燕乐之具。而易曰饮食必有讼。有讼则不可以乐矣。此君子所以不得不谨于饮食之间。而羊羹之致丧师。鼋鼎之致乱邦。亦其明验也。需为饮食之象。而受之以讼者。亦欲先谨于饮食之微也。易诗人之意。从可知也。
天保
御制条问曰。天保定尔之定。注无所释。何也。定是宁静。即坚固之意。以其下有固字。其义无待于释欤。
臣对曰。定字之注无所释。诚未可晓。若曰坚固之意。则下固字恐意叠。大学定静之定。乃知有定向之谓。则是一字之意也。此定字似与大学通。曹粹中曰。保则不危。定则不倾。此亦一定不易之意。而大旨所云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0H 页
 天之安定我君者。盖谓天之降福于君。自有保安一定之理也。定是定也。更无他可释之辞。故注无所释者此耶。
天之安定我君者。盖谓天之降福于君。自有保安一定之理也。定是定也。更无他可释之辞。故注无所释者此耶。采薇
御制条问曰。此遣戍役之诗。是泛言之也。实则未尝不及将帅。以篇中君子之车。君子所依等语观之。可见。小注彭氏说恐非是。未知如何。
臣对曰。未有无军之将。亦未有无将之军。戍卒亦有将之卒也。当其劳遣戍役之时。岂有不及将帅之理乎。故大旨不曰遣戍卒。而泛称戍役。可见将帅之亦在其中。况戎车四牡。皆将帅之所乘也。奚但君子二字为将帅之明验乎。小注彭氏说其无所据。诚如 圣教。
御制条问曰。曰归曰归。岁亦暮止。只是念归期之远也。严华谷以为示归期以安其心。恐非本旨。以下章我行不来观之。何得以安其心乎。
臣对曰。古者戍役。两期而还。采薇之作。当在春暮。则岁暮曰归之期。乃指明年冬也。此为归期之远而忧劳之也。严华谷所谓示归期以安其心者。恐非本旨。两期而还。既有定宪则戍役之所先知也。何待示之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0L 页
 而知之。知其期之将迫。则必有一日三秋之思。而正如行旅临归。自觉乡思之倍切矣。其心尤当不安矣。下章我行不来。亦出于竭力致死。安于其义也。虽有归期。顾何足安其心乎。临昌武曰。天下事不期而骤遭。则情必至于难堪。故预道其契阔之穷苦。道途之险阻。使之前知其必然而当之。则其心可以安矣。此诚好矣。
而知之。知其期之将迫。则必有一日三秋之思。而正如行旅临归。自觉乡思之倍切矣。其心尤当不安矣。下章我行不来。亦出于竭力致死。安于其义也。虽有归期。顾何足安其心乎。临昌武曰。天下事不期而骤遭。则情必至于难堪。故预道其契阔之穷苦。道途之险阻。使之前知其必然而当之。则其心可以安矣。此诚好矣。白华
御制条问曰。笙诗之有声无词。终是疑案。孔子删三千诗为三百十一篇。何必取无词之诗以充其数耶。或曰。删诗未亡而汉后亡之。未知果然否。
臣对曰。笙诗之有声无词。诸儒论说。不胜其纷纭。而盖笙乐奏歌。本有有声无词之不同。则此古乐谱之所存也。当夫子删述之时。不可以无词。并与其篇题而废焉者。正如鲁鼓薛鼓亦有声无词。而尚载礼记投壶篇末之意也。若与篇题而并删去。则千载之下。谁知有有声无词之乐歌乎。然则夫子不删。非为三百篇充数之计。而欲为传谱于后世也。郑康成所谓孔子论诗。雅颂得其所。遭战国秦汉之世而亡之云者。似非的论。而诗之载于传记。如绘事后素。偏其反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1H 页
 而等篇。此固有词之诗而汉后之所亡也。笙诗之无词。非失亡之也。乃本亡也。非如逸诗之亡失。则其非夫子删时之亡。而自古乐谱所无之词也明矣。
而等篇。此固有词之诗而汉后之所亡也。笙诗之无词。非失亡之也。乃本亡也。非如逸诗之亡失。则其非夫子删时之亡。而自古乐谱所无之词也明矣。南有嘉鱼
御制条问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大旨曰。似比而实兴也。何以谓之似比。岂以美实之累于木。固结而不可解。犹宾主之情相结而言欤。
臣对曰。甘瓠之累樛木。吕东莱以为似比而实兴。朱子取之。盖樛木下垂。如主人之卑礼以招客也。甘瓠之上累。如宾客之来从也。此所谓似比也。故朱公迁曰。宾主之相绸缪缱绻亦若此。故以相得之意起兴。以此观之。美实之累于木。固结而不可解。正如宾主之情相结而不可解者非耶。
南山有台
御制条问曰。此诗中君子。以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观之。似指贤者。而以民之父母观之。似指王者。此恐可疑。邦家之基。王业之巩固也。邦家之光。君德之辉光也。所称君子。皆指王者而言欤。乐只君子。本是自下颂上之辞。而集传以君子作宾客。何欤。鱼丽之君子。既指主人。则此君子似亦指主人欤。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1L 页
 臣对曰。民之父母。皆为王者之称。而未见有人臣之称。则此君子似指王者而言者。诚如 圣教。而上二章。皆以贤者称君子。则此一章。独以王者称之者。似未免横决之叹。故程子曰。君子养人如父母。朱氏曰。民之父母。谓爱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推此二说则贤者养人。爱利及民。而民之瞻依其贤者如父母也。如后世之令长有爱民之实。则有召父杜母之称。须以贤者当之似宜。鱼丽之君子。虽指主人。而此君子。集传作宾客。当从集传矣。
臣对曰。民之父母。皆为王者之称。而未见有人臣之称。则此君子似指王者而言者。诚如 圣教。而上二章。皆以贤者称君子。则此一章。独以王者称之者。似未免横决之叹。故程子曰。君子养人如父母。朱氏曰。民之父母。谓爱利及民。民所瞻依者也。推此二说则贤者养人。爱利及民。而民之瞻依其贤者如父母也。如后世之令长有爱民之实。则有召父杜母之称。须以贤者当之似宜。鱼丽之君子。虽指主人。而此君子。集传作宾客。当从集传矣。御制条问曰。南山有枸。朱子曰。枸。枳枸。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长数寸。啖之甘美如饴。内则椇。郑注椇。枳椇。正义椇。藜属。曲礼椇。郑注椇枳也。正义。椇。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可食。椇枸音相近。则枳枸,枳椇似是一物。形如珊瑚。味甜。与大如指长数寸。啖之如饴。又相符合。枸椇之为一物似无疑。而但礼正义之两处异释。为可疑。所贵乎学诗者。以其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也。愿闻博物之论。
臣对曰。枸之为枳枸。朱子盖取释木文陆玑疏语。而为集传者也。与正义中白石李之形味又相符合。而枸与椇音亦相近。枸椇之为一物似无疑。但礼正义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2H 页
 之两处异释。殊未可晓。按曲礼曰。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又枳也。此则以果言。又曰。殷俎名。足间横木。为曲桡之形。如椇枳之树枝。故名椇。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橛。殷以椇。周以房俎。此则以木言。此所以礼之释。两处各异耶。正义藜属之说。无他考證。而藜是草名。枸是木名。以藜解之。恐无义。宋玉疏。曰枳枸来巢。则枸木多枝而曲。本草注。立木也。庄子。若橛株枸。诸说甚多。而朱子又曰味甘。能解酒毒。人家前后左右。有此木则酝酒不成。本草。以木作屋。屋中酒味薄。朱子论其形色性味之详如此。则庶可知之。而今无以就质。良可恨也。
之两处异释。殊未可晓。按曲礼曰。妇人之挚。椇榛脯脩枣栗又枳也。此则以果言。又曰。殷俎名。足间横木。为曲桡之形。如椇枳之树枝。故名椇。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橛。殷以椇。周以房俎。此则以木言。此所以礼之释。两处各异耶。正义藜属之说。无他考證。而藜是草名。枸是木名。以藜解之。恐无义。宋玉疏。曰枳枸来巢。则枸木多枝而曲。本草注。立木也。庄子。若橛株枸。诸说甚多。而朱子又曰味甘。能解酒毒。人家前后左右。有此木则酝酒不成。本草。以木作屋。屋中酒味薄。朱子论其形色性味之详如此。则庶可知之。而今无以就质。良可恨也。蓼萧
御制条问曰。是以有誉处。集传曰。处。安乐也。或曰。处。居也。是言于声誉而居之也。此说如何。
臣对曰。誉处之处。郑笺,孔疏。皆以为使声誉常处天子也。此以处为居之意。而若曰使天子居于声誉。则当曰处誉。而曰誉处者。句法倒。若曰使声誉处于天子。则语脉倒。于斯二者。难免倒错之嫌。故朱子之不取。必以是也。终不如以善誉之安乐为训。故集传所云。盖以此也。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2L 页
 御制条问曰。为龙为光。或引白虎通之文。以为古者诸侯。封不过百里。象雷声。震为龙。故以诸侯为龙。天子有诸侯。犹天之有三光。故以诸侯为光。此说虽似新巧而反觉无味。盖以得见君子为龙光。则其喜之甚可知。其德之美亦可见。意味自好。集传说恐不可易。未知如何。
御制条问曰。为龙为光。或引白虎通之文。以为古者诸侯。封不过百里。象雷声。震为龙。故以诸侯为龙。天子有诸侯。犹天之有三光。故以诸侯为光。此说虽似新巧而反觉无味。盖以得见君子为龙光。则其喜之甚可知。其德之美亦可见。意味自好。集传说恐不可易。未知如何。臣对曰。诗之言宠。以龙字通用。如何天之龙是也。此龙字亦当以宠字解之。至如白虎通之文。虽似新巧而反觉无味。诚如 圣教矣。汉世诸儒。掇拾班,贾馀绪。跌宕经传。奏之白虎阁者。皆尚奇巧新异之论。故多失经传之本旨。何足尽信。
御制条问曰。寿考不忘。是言君子寿考而自不忘其德。老而不懈之意耶。是言君子寿考。使我不忘也欤。
臣对曰。寿考不忘。当属君子自不忘其德也。表记曰。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数之不足。此老而不懈之意也。不必以一句分作两截。以寿考属君子。以不忘属使我看也。
湛露
御制条问曰。左传。齐侯使陈敬仲饮。敬仲辞曰。臣卜其昼。不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以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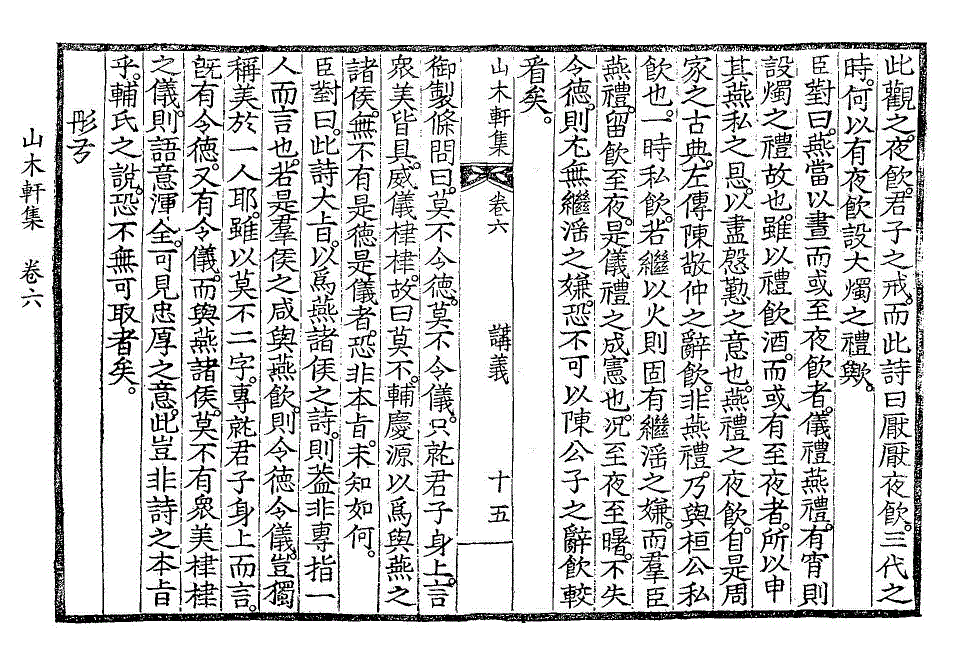 此观之。夜饮。君子之戒。而此诗曰厌厌夜饮。三代之时。何以有夜饮设大烛之礼欤。
此观之。夜饮。君子之戒。而此诗曰厌厌夜饮。三代之时。何以有夜饮设大烛之礼欤。臣对曰。燕当以昼而或至夜饮者。仪礼燕礼。有宵则设烛之礼故也。虽以礼饮酒。而或有至夜者。所以申其燕私之恩。以尽慇勤之意也。燕礼之夜饮。自是周家之古典。左传陈敬仲之辞饮。非燕礼。乃与桓公私饮也。一时私饮。若继以火则固有继淫之嫌。而群臣燕礼。留饮至夜。是仪礼之成宪也。况至夜至曙。不失令德。则尤无继淫之嫌。恐不可以陈公子之辞饮较看矣。
御制条问曰。莫不令德。莫不令仪。只就君子身上。言众美皆具。威仪棣棣。故曰莫不。辅庆源以为与燕之诸侯。无不有是德是仪者。恐非本旨。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诗大旨。以为燕诸侯之诗。则盖非专指一人而言也。若是群侯之咸与燕饮。则令德令仪。岂独称美于一人耶。虽以莫不二字。专就君子身上而言。既有令德。又有令仪。而与燕诸侯。莫不有众美棣棣之仪。则语意浑全。可见忠厚之意。此岂非诗之本旨乎。辅氏之说。恐不无可取者矣。
彤弓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3L 页
 御制条问曰。大旨所云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似指汉高祖盟誓山河而菹醢韩,彭者。而小注。只举唐德宗,昭宗事何欤。下端印刓不与。乃指项羽事。则此段之为指汉高。似益明甚。未知如何。
御制条问曰。大旨所云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似指汉高祖盟誓山河而菹醢韩,彭者。而小注。只举唐德宗,昭宗事何欤。下端印刓不与。乃指项羽事。则此段之为指汉高。似益明甚。未知如何。臣对曰。汉高真三代之下英杰之主。而山河之盟。犹不足为中心贶之。则韩,彭之菹醢。正为朝铁券暮屠戮之明證矣。至若德宗,昭宗。不过唐家之庸主。则李怀光,王行瑜之事。其视汉高。不足深论。小注之只举唐宗。不言汉高。诚为可疑。但上之而兵赐弄臣。以汉哀当之。下之而印刑不与。以项羽当之者。皆许谦之说。而独此一条。出自刘瑾。瑾是金刀之云仍。则此或非为亲者讳之义耶。然则论唐宗。亦可推知于汉高。项羽虽曰汉高之敌。据上段唐宗事。已可推知。则何待下段项羽之论而后知之也。
菁菁者莪
御制条问曰。菁菁者莪。只是兴之不取义者。而后世以为乐育英才之义。岂朱子前说尝作比义者如此欤。韩昌黎亦尝引之。以喻人才之盛。是本于旧说欤。
臣对曰。诗之起兴。亦有取义之辞。而至于此诗本旨。则只是泛言引兴。而旧说育才之取比。失其燕宾之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4H 页
 本意。故朱子改比为兴。其意盖欲人活看也。若其未改之前则其作比意者。果未知如何取义。而但所比者。他无可据。或亦从毛说耶。昌黎引喻。既在朱子之前。则其为本于旧说。与孔疏似无异同矣。
本意。故朱子改比为兴。其意盖欲人活看也。若其未改之前则其作比意者。果未知如何取义。而但所比者。他无可据。或亦从毛说耶。昌黎引喻。既在朱子之前。则其为本于旧说。与孔疏似无异同矣。御制条问曰。前两章既改为兴。则末章之独存比说。何欤。载沉载浮。未定也。我心则休。已定也。不当以未定比已定。故集传以为比未见君子而心不定也。未见君子。是追言之意。而包在正文之中者。则引彼物以喻包在之意。与他诗比例不同。恐不如并此章作兴说。未知如何。
臣对曰。载沉载浮。同为舟未定之状。则正如君子未见之时心不定之义也。以舟之未定。喻心之定。固为比例。而今以未定之舟。谓喻已定之心。则语意矛盾。于比兴俱无所属。无宁以包在之意引物为喻。无失其比例也。
六月
御制条问曰。六月兴师。急于征讨而不畏暑也。如诸葛武侯五月渡泸亦此意。猃狁孔炽。炽字当详味。盖炽是火焰之烈也。言猃狁之乱。如火之炽。甚于炎热之可畏。故用是为急而不恤触暑也。如是看。未知如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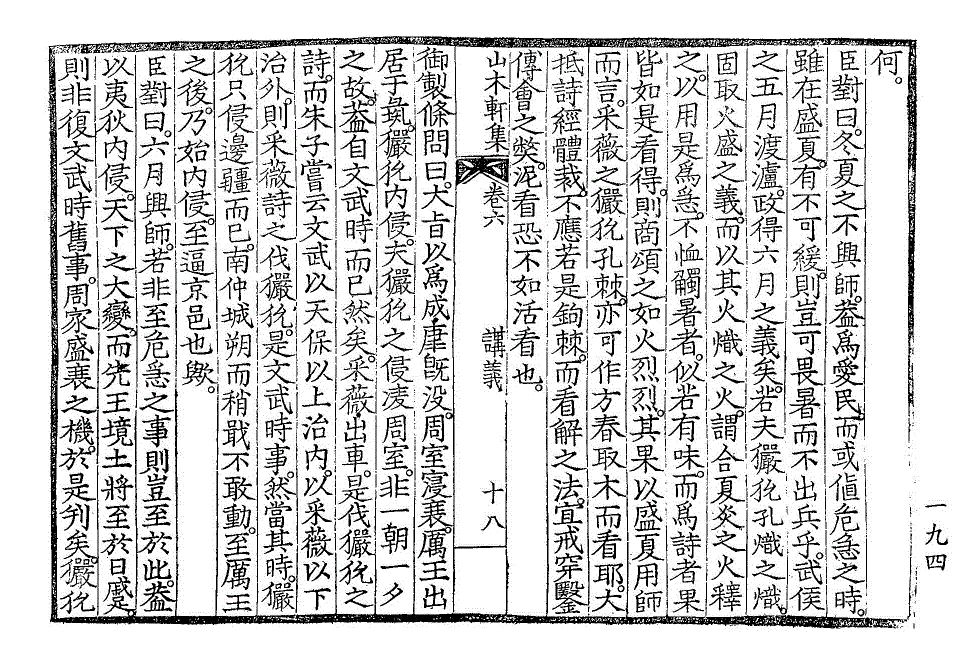 何。
何。臣对曰。冬夏之不兴师。盖为爱民。而或值危急之时。虽在盛夏。有不可缓。则岂可畏暑而不出兵乎。武侯之五月渡泸。政得六月之义矣。若夫猃狁孔炽之炽。固取火盛之义。而以其火炽之火。谓合夏炎之火释之。以用是为急。不恤触暑者。似若有味。而为诗者果皆如是看得。则商颂之如火烈烈。其果以盛夏用师而言。采薇之猃狁孔棘。亦可作方春取木而看耶。大抵诗经体裁。不应若是钩棘。而看解之法。宜戒穿凿傅会之弊。泥看恐不如活看也。
御制条问曰。大旨以为成,康既没。周室寖衰。厉王出居于彘。猃狁内侵。夫猃狁之侵凌周室。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文武时而已然矣。采薇,出车。是伐猃狁之诗。而朱子尝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则采薇诗之伐猃狁。是文武时事。然当其时。猃狁只侵边疆而已。南仲城朔而稍戢不敢动。至厉王之后。乃始内侵。至逼京邑也欤。
臣对曰。六月兴师。若非至危急之事则岂至于此。盖以夷狄内侵。天下之大变。而先王境土将至于日蹙。则非复文武时旧事。周家盛衰之机。于是判矣。猃狁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5H 页
 侵凌。粤自文武而然。则虽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内修外攘之治。自有其道。故虽曰侵凌。而只为疆场之忧而已。及夫采薇之废而骎骎入内。至于厉王之世。莫可禁遏。遂为天下无穷之患者。皆由于先王教化之衰也。倘无中兴拨乱之功。则陆沉之变。不待今日而始然。臣于此尤增京周之思。而窃不胜慨痛矣。
侵凌。粤自文武而然。则虽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内修外攘之治。自有其道。故虽曰侵凌。而只为疆场之忧而已。及夫采薇之废而骎骎入内。至于厉王之世。莫可禁遏。遂为天下无穷之患者。皆由于先王教化之衰也。倘无中兴拨乱之功。则陆沉之变。不待今日而始然。臣于此尤增京周之思。而窃不胜慨痛矣。御制条问曰。共武之服。或曰。共非供。即同也。武即戎也。服非事。即衣也。言将帅同此戎衣也。上章既曰常服。又曰我服。皆称戎服。岂于此章服字。独称事乎。此说亦通。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章共武之服。集传所释。断不可以他说容改。如作或说。以将帅同此戎衣而看解。则上章常服。即靺韦之上下同服。此不必叠言同服之义。又其既成我服者。亦以其即成戎服而解之耶。虽连上句有严有翼之文而看之。严敬莅兵。正好作将帅之德。若以衣服释之。有何严翼之可言乎。
御制条问曰。整居焦获之整字可疑。此诗方专言我师军容之盛。而却于彼寇之兵。以整齐称之何欤。夷狄之兵。宜若乱无统纪。而乃能大众整齐。则其为强寇可知。强寇之难制。而能讨平之。尤见功大。故言之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5L 页
 如此欤。
如此欤。臣对曰。此云整居。即整齐安排之意。未必以军容整肃而言也。盖其猾夏之势既自孔炽。而盘据焦获。以为安排久处之计。时出轻军。侵袭于镐方泾阳之间。则可见敌势之整齐而难制也。以此为说。盖欲示能讨强冠之功者。诚如 圣教矣。
御制条问曰。末章。辅庆源以为吉甫既归而私自与朋友燕饮而已。非宣王燕之也。盖言宣王燕之。则吉甫之友。不得以与也。然吉甫之燕。安知非宣王赐燕于其家如后世之礼。而张仲得以宾友而与焉者欤。
臣对曰。其曰吉甫燕喜。则此非侍燕于君。而私自燕饮。可以见矣。若张仲之与宴则固无御宴私宴之别。虽侍燕于宣王。在群臣尚可共饮。况以吉甫同德之友。而为宣王孝友之臣者莫如张仲。而岂不与于是燕乎。然而既自吉甫而言。则其为私燕无疑矣。
采苞
御制条问曰。师干。集传曰。干。捍也。是言习师众捍御之事。然或说以为师干之试。犹言兵器之试。干只当直作盾字释。此说何如。
臣对曰。干之训捍。亦取其干盾之捍。盖以师众而捍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6H 页
 御。取喻于干盾之捍御也。若或者之说则以此师干之试。直谓兵器之试。此于为诗。恐非不以辞害义之意。如作兵器看则只举一干。而岂可谓尽试诸般之兵器耶。且此是美方叔师纪之盛。则只当以鍊习御敌之义看之。恐得矣。
御。取喻于干盾之捍御也。若或者之说则以此师干之试。直谓兵器之试。此于为诗。恐非不以辞害义之意。如作兵器看则只举一干。而岂可谓尽试诸般之兵器耶。且此是美方叔师纪之盛。则只当以鍊习御敌之义看之。恐得矣。车攻
御制条问曰。宣王。贤王也。云汉之侧身。庭燎之勤政。无非中兴之基本。而朱子独以车攻为中兴之势者何欤。
臣对曰。宣王中兴之功。其本虽在于畏天勤政。而其成效则实资于车马师徒之事。如云汉,庭燎等诗。但美其敬惧靡怠之德。则以此谓基本之在此。固可也。直谓以此乃中兴之诗则其可乎。至于此章之词。其所美车马之盛。纪律之严。可谓善形容重恢之功。朱子之舍彼取此。盖有以也。
御制条问曰。大庖不盈。君道也。取民有制。损上益下。举此事而可见也。旧说之以不作岂不。虽似亦通。而其合于君人之大道。则不如前说。故朱子不取欤。
臣对曰。损上益下。人君之大道。则大庖不盈。当以不字看。古者获禽而有三不献之规。献之而有三取一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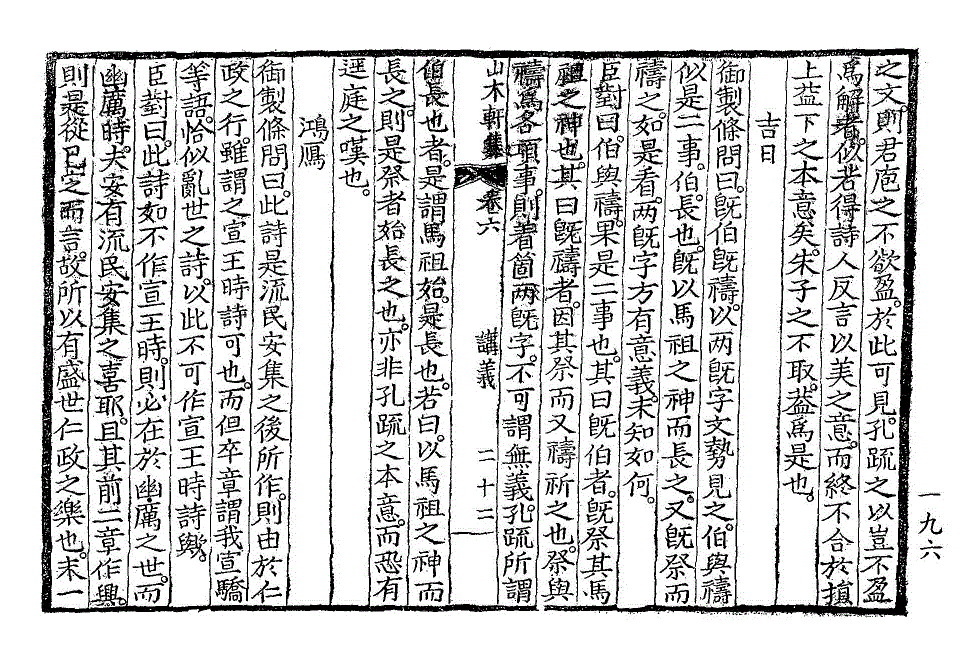 之文。则君庖之不欲盈。于此可见。孔疏之以岂不盈为解者。似若得诗人反言以美之意。而终不合于损上益下之本意矣。朱子之不取。盖为是也。
之文。则君庖之不欲盈。于此可见。孔疏之以岂不盈为解者。似若得诗人反言以美之意。而终不合于损上益下之本意矣。朱子之不取。盖为是也。吉日
御制条问曰。既伯既祷。以两既字文势见之。伯与祷似是二事。伯。长也。既以马祖之神而长之。又既祭而祷之。如是看。两既字方有意义。未知如何。
臣对曰。伯与祷。果是二事也。其曰既伯者。既祭其马祖之神也。其曰既祷者。因其祭而又祷祈之也。祭与祷为各项事。则着个两既字。不可谓无义。孔疏所谓伯长也者。是谓马祖始。是长也。若曰。以马祖之神而长之。则是祭者始长之也。亦非孔疏之本意。而恐有径庭之叹也。
鸿雁
御制条问曰。此诗是流民安集之后所作。则由于仁政之行。虽谓之宣王时诗可也。而但卒章谓我宣骄等语。恰似乱世之诗。以此不可作宣王时诗欤。
臣对曰。此诗如不作宣王时。则必在于幽,厉之世。而幽,厉时。夫安有流民安集之喜耶。且其前二章作兴。则是从已定而言。故所以有盛世仁政之乐也。末一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7H 页
 章作比。则是追言其未集时流散之劳而言。故所以有乱世怨苦之情也。安集之喜。虽在宣王之时。而其前流散之苦。其为厉王暴乱之日可知。则岂可以此谓非宣王时诗乎。若大旨下段所谓未见其为宣王诗。则亦未知其何所指也。
章作比。则是追言其未集时流散之劳而言。故所以有乱世怨苦之情也。安集之喜。虽在宣王之时。而其前流散之苦。其为厉王暴乱之日可知。则岂可以此谓非宣王时诗乎。若大旨下段所谓未见其为宣王诗。则亦未知其何所指也。复对曰。观于其究安宅等语。此诗之作于宣王时无疑矣。末章云云。特追言未集时流散之劳。故语势不得不如此耳。
庭燎
御制条问曰。读书者。多疑庭燎非宣王时之诗。盖以在鸿雁诗之下也。然庭燎终似宣王时诗。无乃与吉日,车攻相连。当在鸿雁诗之上。而编入时或失次序欤。
臣对曰。庭燎之谓宣王时作。多以烈女传姜后事为證。而以诗意观之。似不待脱簪之谏而先自问之。则此亦未足为明验。然而读其诗。亦可以论其世。此诗既在变雅之间则必是成,康以后之诗。而以时君历数。勤于政事者未有如宣王之贤。则此为宣王时作恐无疑。或以在鸿雁诗之下为疑。而此亦有不然者。所谓鸿雁诗。既是安集流民。有可见仁政之下究。则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7L 页
 其非宣王时作。亦安可必也。然则编时失序。又不可定其必然。而终当作宣王之诗。似明的矣。
其非宣王时作。亦安可必也。然则编时失序。又不可定其必然。而终当作宣王之诗。似明的矣。鹤鸣
御制条问曰。二章圈注载程子说。夫四者之事。集传所释。独详于他山之石一语。何也。岂此诗即君子忧谗而作故欤。
臣对曰。此诗四物之取譬莫非亲切。而最其他山之石一端语。不但为君子忧谗者切喻。于吾人为己之学。引而伸之。触类以长。则实亦有反躬自修之益。集传之所以特取程子之说。而表出于别圈之下者。盖有以也。
祁父
御制条问曰。使母尸饔。可知其无昆弟矣。宣王之有愧于越句践,魏无忌何欤。宣王于是乎未免一失。而当时如尹吉甫,仲山甫辈。不能谏止。何欤。
臣对曰。此诗之失。不但使孤子而从戎违养者有愧于句践,无忌。圻封虎贲之士远出征役。又乖先王之制。则曾谓宣王之修复旧典而有此事乎。序以此诗及白驹。皆谓刺宣王而作。朱子以为宣王始任申,仲,方,召之贤。而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号文公之徒谏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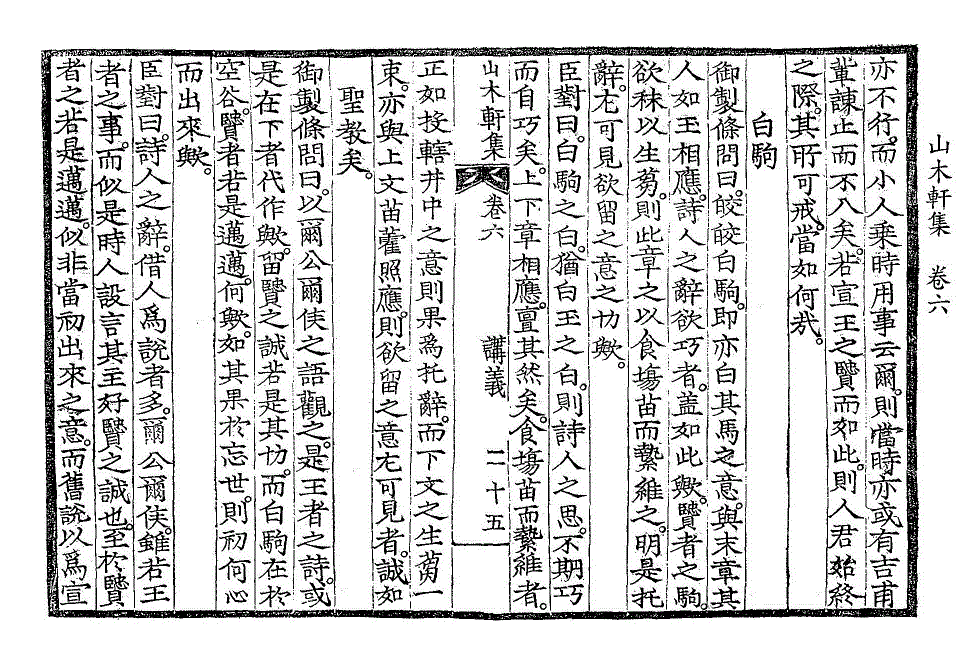 亦不行。而小人乘时用事云尔。则当时亦或有吉甫辈谏止而不入矣。若宣王之贤而如此。则人君始终之际。其所可戒。当如何哉。
亦不行。而小人乘时用事云尔。则当时亦或有吉甫辈谏止而不入矣。若宣王之贤而如此。则人君始终之际。其所可戒。当如何哉。白驹
御制条问曰。皎皎白驹。即亦白其马之意。与末章其人如玉相应。诗人之辞欲巧者。盖如此欤。贤者之驹。欲秣以生刍。则此章之以食场苗而絷维之。明是托辞。尤可见欲留之意之切欤。
臣对曰。白驹之白。犹白玉之白。则诗人之思。不期巧而自巧矣。上下章相应。亶其然矣。食场苗而絷维者。正如投辖井中之意则果为托辞。而下文之生刍一束。亦与上文苗藿照应。则欲留之意尤可见者。诚如 圣教矣。
御制条问曰。以尔公尔侯之语观之。是王者之诗。或是在下者代作欤。留贤之诚若是其切。而白驹在于空谷。贤者若是迈迈。何欤。如其果于忘世。则初何心而出来欤。
臣对曰。诗人之辞。借人为说者多。尔公尔侯。虽若王者之事。而似是时人设言其主好贤之诚也。至于贤者之若是迈迈。似非当初出来之意。而旧说以为宣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8L 页
 王好贤之诚始勤终怠。则盖其任贤使能。周室中兴。即是初年事。及其末年。乃反不肯用贤。故诗人之意。似指宣王初晚之异而起咏也。此岂贤者果于忘世而然乎。
王好贤之诚始勤终怠。则盖其任贤使能。周室中兴。即是初年事。及其末年。乃反不肯用贤。故诗人之意。似指宣王初晚之异而起咏也。此岂贤者果于忘世而然乎。斯干
御制条问曰。首章之辞。或以为非谓室之已成。临水面山。其固如竹苞松茂。是落成燕饮。而追叙其未为室之时经营相度。而言是地有水有山有松有竹。可以为室。此说如何。
臣对曰。临水面山。竹苞松茂。是言地势之壮。盘基之厚则筑室落成之后。状出其所见。似无可疑。或者所谓追叙未为室之时者。未知何所据也。况下句兄弟相好。亦居是室者颂祷之词。则于此尤可见其为落成后形容得也。或说恐无义。
御制条问曰。熊罴虺蛇为男女之祥。是筑室之后。果有是梦欤。严华谷云设为之辞。然则诗人自以意见创设如此欤。无乃古者有占梦之书。明言其兆。分属男女。故诗人据而为言欤。
臣对曰。熊罴叶梦。乃生男女之祥。则此亦颂祷之词也。盖言入此室处。必有吉梦。而兄弟相好之馀。子孙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9H 页
 亦为昌炽之兆矣。是岂筑室之后果即有吉梦而然乎。严华谷所云设为之辞者。果得诗人之意。而若其熊罴之为男。虺蛇之为女。即以阴阳之理得男女之分也。占梦之书。臣虽未见。而诗人据以为说者。亦必以阴阳之理推得也。
亦为昌炽之兆矣。是岂筑室之后果即有吉梦而然乎。严华谷所云设为之辞者。果得诗人之意。而若其熊罴之为男。虺蛇之为女。即以阴阳之理得男女之分也。占梦之书。臣虽未见。而诗人据以为说者。亦必以阴阳之理推得也。无羊
御制条问曰。牧人之梦。朱子既云未详。姑以或说解之。而小注阴阳和则鱼多云者可疑。阴阳和则无物不蕃。岂独鱼为多欤。
臣对曰。占梦之说。朱子曰未详。亦出于阙疑之意。则固无论已。试以或说主之。毛说足之。埤雅参之。阴阳和则鱼多者。毛氏之论。而埤雅则曰。春鱼遗种泥中。至明年水及则化鱼。日暴则为蝗。阴阳和。雨旸若则鱼多。合二说而论之。槩是丰年梦鱼之验。而或说之意。于是乎著矣。况此诗是考牧之诗。而陆而羊牛腯。水而鱼族多则阴阳之和可知。阴阳和则庶物之蕃可知。驺虞章之观一发五𤡆。而知禽兽之蕃息者。岂非此意乎。
节南山
御制条问曰。维石岩岩。或云岩险之意。以比尹氏之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199L 页
 不平。民具尔瞻。盖言尹氏之为恶。众目所睹而不可掩。此说如何。
不平。民具尔瞻。盖言尹氏之为恶。众目所睹而不可掩。此说如何。臣对曰。不曰维山岩岩。而曰维石岩岩。则岩字带得岩险之义。而其所起兴。亦指师尹之不平。则岩险是不平之意也。且其具瞻二字。若以十目所视之意当之。则语意尤有味。或说似得之。
御制条问曰。前章既言不躬不亲。此又言不自为政。若使尹氏躬自为政则庶免病国。而惟其所任用者小人。故致此大乱欤。
臣对曰。自古小人之窃弄国柄者。必引用一边不好底人以自树党。故朱子曰。尹氏只是一个不好人。而所任用姻娅之人。是几个不好人。然则虽使尹氏不任小人而亲自为政。不免为病国之人。而特其招朋引类。助桀为虐耳。若使尹氏本非不好之人。则所任用者亦非不好之人。其终致乱。是尹氏之自致也。夫岂任用者之所致哉。
正月
御制条问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我东先儒以为注解未甚的当。恐是言自家枢机之难慎。一不择发。祸辄随之。所以有忧怯之意。反为彼所侮云尔。若解作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0H 页
 他人之言。则与上句呼父母而叹身世。似不吻协。此论如何。
他人之言。则与上句呼父母而叹身世。似不吻协。此论如何。臣对曰。人之讹言。虚伪反覆。惟其虚伪。故善言恶言为不足喜怒。而惟其反覆。故我之所以处之也难。是以。忧之甚而至于病。则反为彼之所侵侮也。若以好言莠言看作自家枢机之难慎。则此虽兴戎出好之戒。而我之所以慎枢机而忧其祸随者。有何为彼侵侮之义乎。是故。朱丰城以好言莠言看作他人言者。固是矣。我东先儒所谓自家枢机之论。恐与本旨矛盾。
十月之交
御制条问曰。先儒云十月之章。唐志曰。以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以此观之。正月篇在此诗之上。非东迁后之诗明矣。朱子犹置或说于传疑之例。何欤。
臣对曰。唐志所云幽王六年之说。李三山引以为解者必有考證。则正月之非东迁以后诗明矣。古今历年之数。汉儒以下争说纷纭。未可适从。故朱子姑置或说。以存传疑之意。似无别般旨义。
雨无正
御制条问曰。此诗篇名。终以阙疑处之耶。以正月繁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0L 页
 霜。十月之交观之。雨无正亦是言灾异也。韩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与其下降丧饥馑相协。似当从之。而朱子以十二句与下章长短不齐为不可。窃谓首章旻天疾威。是小旻文而脱简在此。弗虑弗图是衍文。如是断定则只为十句矣。雨无极明为此诗。恐不必以序中所说正大夫刺幽王一款之为误。并疑其信者。未知如何。作此诗者。亦大夫惟正字为讹欤。
霜。十月之交观之。雨无正亦是言灾异也。韩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与其下降丧饥馑相协。似当从之。而朱子以十二句与下章长短不齐为不可。窃谓首章旻天疾威。是小旻文而脱简在此。弗虑弗图是衍文。如是断定则只为十句矣。雨无极明为此诗。恐不必以序中所说正大夫刺幽王一款之为误。并疑其信者。未知如何。作此诗者。亦大夫惟正字为讹欤。臣对曰。此诗篇名。朱子先引欧阳说。断以阙疑。次引元城说。谓似有理。元城之论。盖取韩,毛两诗之意。而朱子犹存之。则其曰雨无其极。正与正月繁霜。十月之交。同为灾异之验也。终不必以阙疑处之也明矣。至若脱简衍文。似不可断定。而若以刘氏说从之。则与序说大相径庭。岂可以序说之误。便疑刘说之可信而同归疑案乎。正大夫三字既在经文。则序说正字之为讹。臣未知其何所指也。
御制条问曰。匪舌是出。维躬是瘁。注解终欠分晓。其详言欤。
臣对曰。此诗之作。即在昏乱之时。而忠佞不分。祸福反易。忠言出于口。则便受不能言之讥。而适足以瘁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1H 页
 其躬矣。其曰匪舌是出者。非但出诸口而受讥于人。乃反病其身矣。注解中非但出诸口之下。着得受讥二字。则似益分晓矣。
其躬矣。其曰匪舌是出者。非但出诸口而受讥于人。乃反病其身矣。注解中非但出诸口之下。着得受讥二字。则似益分晓矣。小旻
御制条问曰。回遹之遹。恐当作谲。遹只是聿字。未见有辟之意。遹之为辟。果有可据耶。似以谲之声音转讹而为遹。未知如何。
臣对曰。遹。大雅文王作聿。此作辟。注解不同。而此章回遹。当作谲。此似声音之转讹者。诚如 圣教矣。
御制条问曰。大舜好察迩言。而此章以听迩言为戒。何欤。
臣对曰。听言之道。在于察之一字。既听而又察则大舜之察迩。而刍荛必择是也。徒听而不能察则此章之听迩。而偏听生奸是也。书不云乎。无稽之言勿听。不询之谋勿庸。
御制条问曰。此诗全篇。以谋之一字为眼目骨子。而至第五章。又并陈肃乂哲谋圣五事。何欤。五事之中。肃乂哲圣四者皆纯好。而谋则有臧否邪正。何欤。谋有臧否邪正。故首章曰。谋犹回遹。次章曰。谋之不臧。此则非五事之谋欤。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1L 页
 臣对曰。国之兴丧。系于谋之得失。故谋为此章之骨子。而箕范之五事。谋为最重。故居中统四。而第五章之并列五事者此也。肃乂哲圣。虽皆好底事。而四者之反。咎徵辄随。则此亦如谋之有臧否。而章内之或圣或否。已言之矣。况前后章之谋字。只是五事中谋字。则谋岂有二致也。
臣对曰。国之兴丧。系于谋之得失。故谋为此章之骨子。而箕范之五事。谋为最重。故居中统四。而第五章之并列五事者此也。肃乂哲圣。虽皆好底事。而四者之反。咎徵辄随。则此亦如谋之有臧否。而章内之或圣或否。已言之矣。况前后章之谋字。只是五事中谋字。则谋岂有二致也。小宛
御制条问曰。螟蛉蜾蠃。式谷似之。盖作诗者欲教其子以是心推之。追思其父母之心。亦欲令己化于善。而不敢忘也。如是看则与上章有怀二人。下章无忝所生。承接紧密。尤似有味。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诗本意。上述思亲之意。下及教子之方。则以其教子之心。追思父母教我之心者。亦天理人情之固然。蜾蠃式谷。盖出教子化善之心。则追思父母亦欲令己化善者。正合诗人之意。若能如是看则上下章承接紧密。诚如 圣教矣。
小弁
御制条问曰。朱子尝云何辜于天。似亦自以为无罪。而及为集传。乃以同之于大舜于我何哉。何欤。
臣对曰。大舜之怨。怨己之不容乎亲也。小弁之怨。怨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2H 页
 亲之不容乎己也。此不可同日而语。其视凯风之不怨。犹为不失亲亲之仁。此所谓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然而我罪伊何一句。与大舜于我何哉之义同。故朱子尝曰。小弁之怨。不为不孝。而乃反同之于集传。盖欲姑取其一节之同。而亦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明矣。
亲之不容乎己也。此不可同日而语。其视凯风之不怨。犹为不失亲亲之仁。此所谓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然而我罪伊何一句。与大舜于我何哉之义同。故朱子尝曰。小弁之怨。不为不孝。而乃反同之于集传。盖欲姑取其一节之同。而亦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明矣。巧言
御制条问曰。君子如祉。集传曰。祉。犹喜也。此以对如怒看。故谓之喜。而不如因其字本义作福禄说。盖曰。见贤者之言。若爱而福之则乱庶几遄已矣。如是为解。未知如何。
臣对曰。喜怒互对。句义恰当。故集传解之。为喜以对如怒。今若因其本字之义。看作福禄说而曰。贤者之言。爱而福之。则不但有欠于喜怒互对之义。语涉深曲。恐未安。
御制条问曰。秩秩。序也。是指道之阶级而言欤。莫。定也。如论语无适无莫之莫。盖言斯道极浩大。岐路易分。趋向难定。圣人定之而后。道乃秩然而有序欤。此二句旨义。愿详闻之。
臣对曰。秩。如天序天秩之秩。言序也。莫。如无适无莫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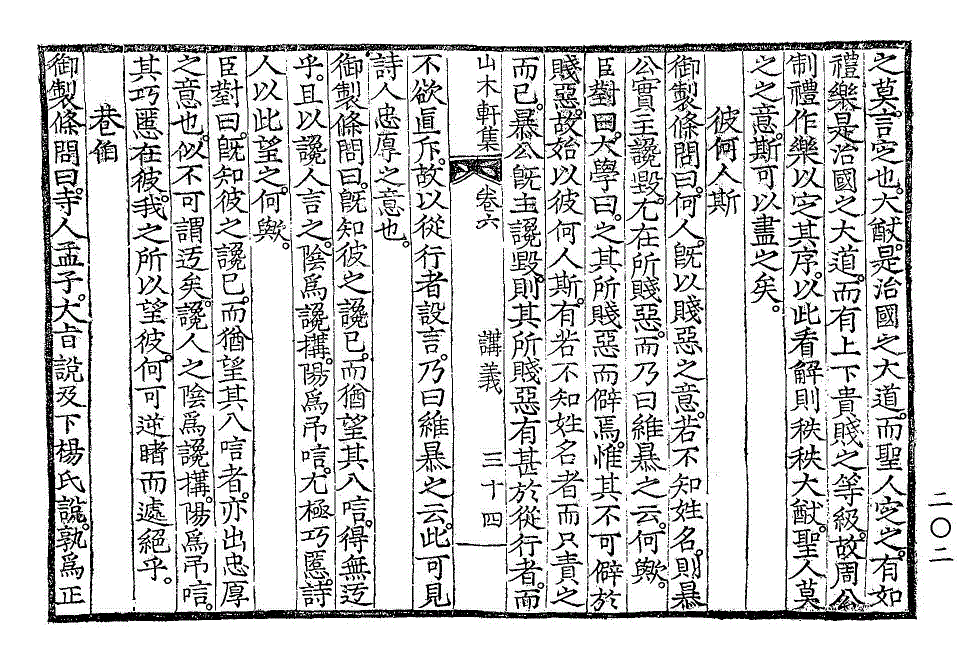 之莫。言定也。大猷。是治国之大道。而圣人定之。有如礼乐是治国之大道。而有上下贵贱之等级。故周公制礼作乐以定其序。以此看解则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之意。斯可以尽之矣。
之莫。言定也。大猷。是治国之大道。而圣人定之。有如礼乐是治国之大道。而有上下贵贱之等级。故周公制礼作乐以定其序。以此看解则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之意。斯可以尽之矣。彼何人斯
御制条问曰。何人。既以贱恶之意。若不知姓名。则暴公实主谗毁。尤在所贱恶。而乃曰维暴之云。何欤。
臣对曰。大学曰。之其所贱恶而僻焉。惟其不可僻于贱恶。故始以彼何人斯。有若不知姓名者而只责之而已。暴公既主谗毁。则其所贱恶有甚于从行者。而不欲直斥。故以从行者设言。乃曰维暴之云。此可见诗人忠厚之意也。
御制条问曰。既知彼之谗己。而犹望其入唁。得无迂乎。且以谗人言之。阴为谗搆。阳为吊唁。尤极巧慝。诗人以此望之。何欤。
臣对曰。既知彼之谗己。而犹望其入唁者。亦出忠厚之意也。似不可谓迂矣。谗人之阴为谗搆。阳为吊唁。其巧慝在彼。我之所以望彼。何可逆睹而遽绝乎。
巷伯
御制条问曰。寺人孟子。大旨说及下杨氏说。孰为正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3H 页
 义欤。
义欤。臣对曰。大旨说。适中谗人浸润之患。而辞正而理顺。杨氏说。兼言内侍专宠之习。而语切而意深。二说固合两存。而但巷伯被宫之后。王后,太子,诸大夫以谗多废。则此为大旨所论之明验矣。至如杨氏说。恐启奄竖专宠自恣。无间可伺。酿成后世恭显之祸。此甚可怕。当以大旨说作正义看。
蓼莪
御制条问曰。大旨。人民劳苦。孝子不得终养而作。夫劳苦云者。是贫穷之谓耶。无财不可以悦。故亲在而不能养。追慕已自痛伤欤。抑其身困于征戍。而不得终孝于其亲欤。
臣对曰。此诗亦在幽王之时。人民劳苦。似是征戍之役矣。幽,厉之时。干戈不息。饥馑荐至。从役者亦岂不困于贫穷。而孝子之不得终养者。一则征戍。二则贫穷。似是从役者贫无以为养。而又为征役之所从。远离父母。故及其亲没之后。追思而痛伤者也。
御制条问曰。鞠畜。皆养也。育亦养。而注释必加覆字。何欤。鞠我育我。重言而复言也。小注。谢叠山引易之育德。孟子之育英才。以解育我之义。则恐非本旨。此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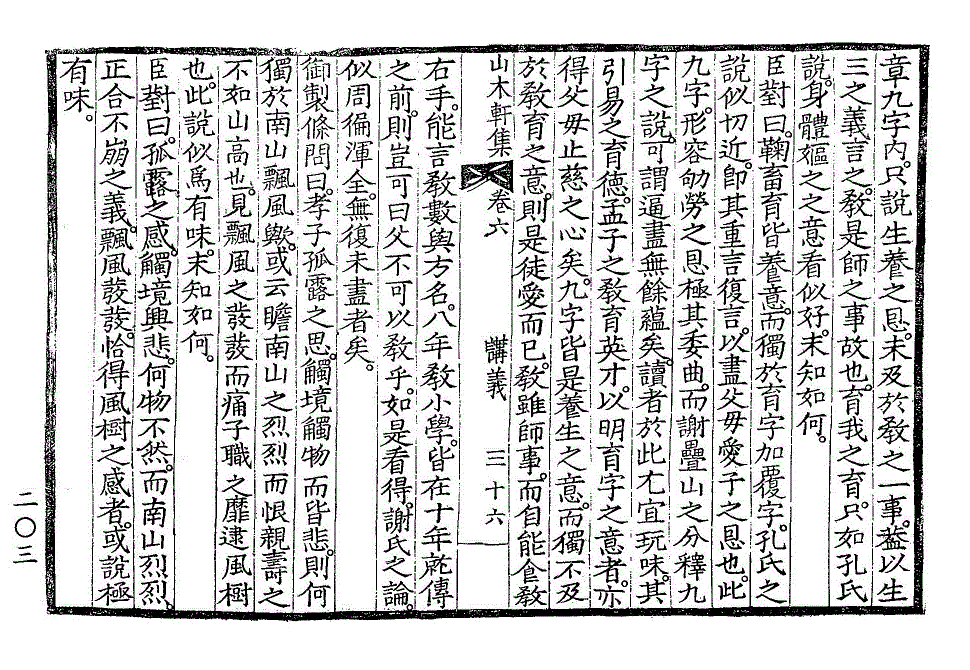 章九字内。只说生养之恩。未及于教之一事。盖以生三之义言之。教是师之事故也。育我之育。只如孔氏说。身体妪之之意看似好。未知如何。
章九字内。只说生养之恩。未及于教之一事。盖以生三之义言之。教是师之事故也。育我之育。只如孔氏说。身体妪之之意看似好。未知如何。臣对曰。鞠畜育皆养意。而独于育字加覆字。孔氏之说似切近。即其重言复言。以尽父母爱子之恩也。此九字。形容劬劳之恩极其委曲。而谢叠山之分释九字之说。可谓逼尽无馀蕴矣。读者于此尤宜玩味。其引易之育德。孟子之教育英才。以明育字之意者。亦得父母止慈之心矣。九字皆是养生之意。而独不及于教育之意。则是徒爱而已。教虽师事。而自能食教右手。能言教数与方名。八年教小学。皆在十年就傅之前。则岂可曰父不可以教乎。如是看得。谢氏之论。似周遍浑全。无复未尽者矣。
御制条问曰。孝子孤露之思。触境触物而皆悲。则何独于南山飘风欤。或云瞻南山之烈烈而恨亲寿之不如山高也。见飘风之发发而痛子职之靡逮风树也。此说似为有味。未知如何。
臣对曰。孤露之感。触境兴悲。何物不然。而南山烈烈。正合不崩之义。飘风发发。恰得风树之感者。或说极有味。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4H 页
 大东
大东御制条问曰。或云跂彼织女。跂非偶也。跂予望之也。睆彼牵牛。睆非明也。睆尔视之也。盖言不得于人而仰求于天。故望视彼二星。此说何如。
臣对曰。跂。企也。睆。明也。或者以企望明见释之者似有味。而若如后世以此二星作夫妇看。若相跂望而思见则此不经之说。恐不可取信也。
四月
御制条问曰。以山有嘉卉为兴。则是言国有残贼之臣。异乎山之有嘉卉也欤。
臣对曰。国有残贼之臣则其无桢干之材可知。见其山之有嘉卉。而叹其国之无桢干。此乃伤时之意也。
北山
御制条问曰。独贤。独劳也。上章曰。偕偕士子。下章曰。膂力方刚。既是强壮之人则足任事务之繁。何惮于劳苦。而必怨之欤。且夫君子之心。不愿佚乐。而诗之言如此者。何欤。
臣对曰。为此诗者。槩多忠厚之辞。则其不以劳佚为恤可知。况是强壮膂力之时。则区区征役。又何惮乎。盖小人而处于逸乐。君子而任其劳瘁。足见时君任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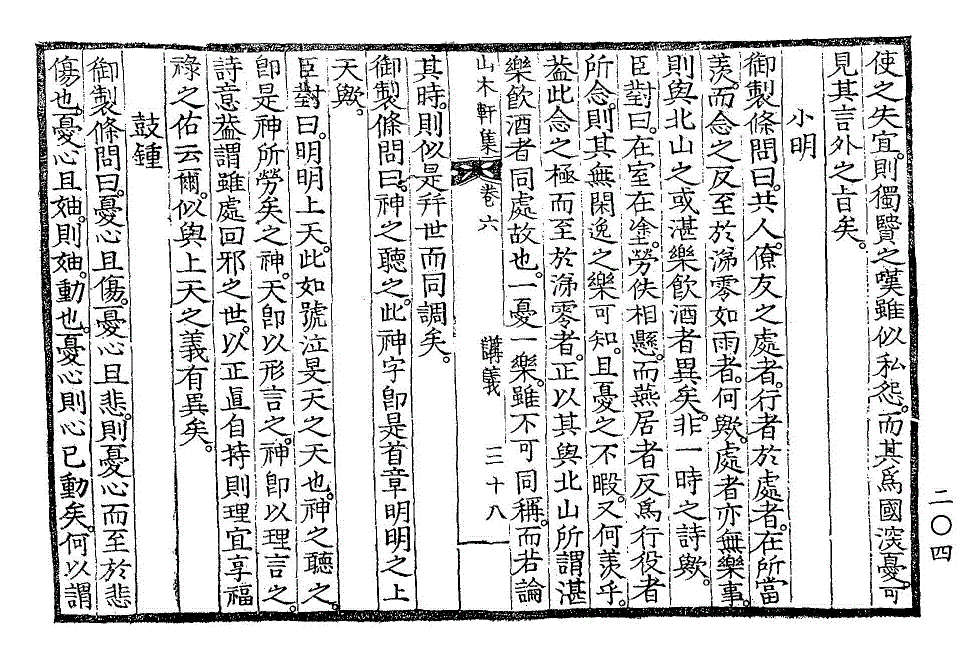 使之失宜。则独贤之叹虽似私怨。而其为国深忧。可见其言外之旨矣。
使之失宜。则独贤之叹虽似私怨。而其为国深忧。可见其言外之旨矣。小明
御制条问曰。共人。僚友之处者。行者于处者。在所当羡。而念之反至于涕零如雨者。何欤。处者亦无乐事。则与北山之或湛乐饮酒者异矣。非一时之诗欤。
臣对曰。在室在涂。劳佚相悬。而燕居者反为行役者所念。则其无闲逸之乐可知。且忧之不暇。又何羡乎。盖此念之极而至于涕零者。正以其与北山所谓湛乐饮酒者同处故也。一忧一乐。虽不可同称。而若论其时。则似是并世而同调矣。
御制条问曰。神之听之。此神字即是首章明明之上天欤。
臣对曰。明明上天。此如号泣旻天之天也。神之听之。即是神所劳矣之神。天即以形言之。神即以理言之。诗意盖谓虽处回邪之世。以正直自持则理宜享福禄之佑云尔。似与上天之义有异矣。
鼓钟
御制条问曰。忧心且伤。忧心且悲。则忧心而至于悲伤也。忧心且妯。则妯。动也。忧心则心已动矣。何以谓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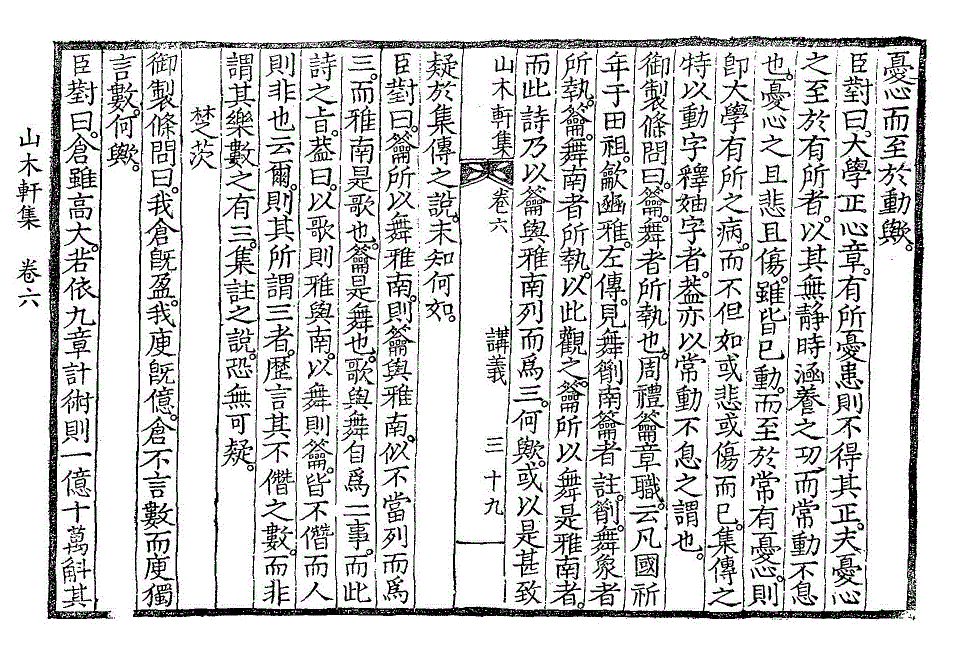 忧心而至于动欤。
忧心而至于动欤。臣对曰。大学正心章。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夫忧心之至于有所者。以其无静时涵养之功而常动不息也。忧心之且悲且伤。虽皆已动。而至于常有忧心。则即大学有所之病。而不但如或悲或伤而已。集传之特以动字释妯字者。盖亦以常动不息之谓也。
御制条问曰。籥。舞者所执也。周礼籥章职。云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左传。见舞箾南籥者注。箾。舞象者所执。籥。舞南者所执。以此观之。籥所以舞是雅南者。而此诗乃以籥与雅南列而为三。何欤。或以是甚致疑于集传之说。未知何如。
臣对曰。籥所以舞雅南。则籥与雅南。似不当列而为三。而雅南是歌也。籥是舞也。歌与舞自为二事。而此诗之旨。盖曰。以歌则雅与南。以舞则籥。皆不僭而人则非也云尔。则其所谓三者。历言其不僭之数。而非谓其乐数之有三。集注之说。恐无可疑。
楚茨
御制条问曰。我仓既盈。我庾既亿。仓不言数而庾独言数。何欤。
臣对曰。仓虽高大。若依九章计术则一亿十万斛其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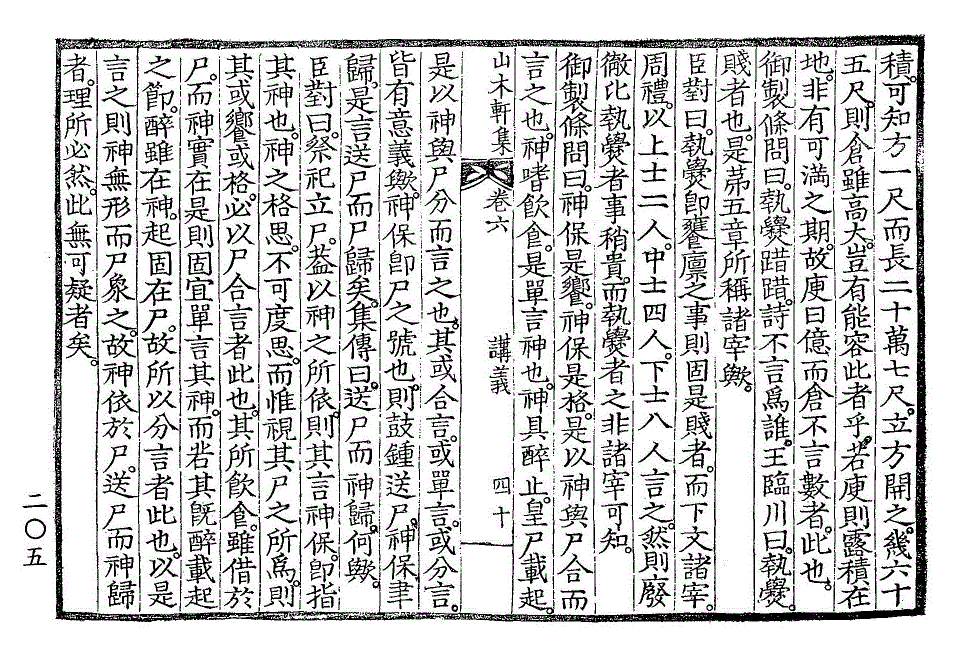 积。可知方一尺而长二十万七尺。立方开之。几六十五尺。则仓虽高大。岂有能容此者乎。若庾则露积在地。非有可满之期。故庾曰亿而仓不言数者。此也。
积。可知方一尺而长二十万七尺。立方开之。几六十五尺。则仓虽高大。岂有能容此者乎。若庾则露积在地。非有可满之期。故庾曰亿而仓不言数者。此也。御制条问曰。执爨踖踖。诗不言为谁。王临川曰。执爨。贱者也。是第五章所称诸宰欤。
臣对曰。执爨即饔廪之事则固是贱者。而下文诸宰。周礼。以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言之。然则废彻比执爨者事稍贵。而执爨者之非诸宰可知。
御制条问曰。神保是飨。神保是格。是以神与尸合而言之也。神嗜饮食。是单言神也。神具醉止。皇尸载起。是以神与尸分而言之也。其或合言。或单言。或分言。皆有意义欤。神保即尸之号也。则鼓钟送尸。神保聿归。是言送尸而尸归矣。集传曰。送尸而神归。何欤。
臣对曰。祭祀立尸。盖以神之所依。则其言神保。即指其神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惟视其尸之所为。则其或飨或格。必以尸合言者此也。其所饮食。虽借于尸。而神实在是则固宜单言其神。而若其既醉载起之节。醉虽在神。起固在尸。故所以分言者此也。以是言之则神无形而尸象之。故神依于尸。送尸而神归者。理所必然。此无可疑者矣。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6H 页
 甫田
甫田御制条问曰。烝我髦士。注曰。髦士。秀民也。古者。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太学。而其馀悉归于农则农夫之中。亦有髦士。何欤。抑其人朝耕夜读。如后世董邵南之类欤。
臣对曰。兴贤兴氓。自是成周之美制。而士出于农。非有二致则凡其入学之秀民。皆是服田之农夫。初无农与士之有殊矣。艺文志亦曰。古之学者。且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则当时朝耕夜读。必有如蕫生之为者矣。
御制条问曰。以我齐明。或曰。齐明即齐明盛服之齐明。非明粢也。齐明。诚也。牺牲。物也。诚与物具备。然后享神之道尽矣。故诗云然。此说何如。
臣对曰。周礼春官齍盛吉洁注。粢。六谷也。六谷揔为齐。左传曰。洁粢。言为谷则洁清。皆与此章齐明之义相符。则其为粢盛之义。更无可疑。若如或说而谓此为诚。则所谓粢盛明洁。亦不可谓诚耶。且以诚而看齐明。则祀享之物。粢盛比诸牺羊较重。何乃独言牺羊而不及粢盛乎。恐非的当之论矣。
御制条问曰。攘其左右。或者之说曰。非取左右之馈。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6L 页
 是攘臂而就也。吕东莱云攘之者。喜之甚取之疾。而不自知其手之捷狎。然则非不可矣。古文左右皆从手。故少仪曰。居之于左。以左为左手矣。檀弓曰。拱而尚右。以右为右手矣。礼仪乡射曰。左右抚矢而乘之。以左右为左右手矣。据此则攘其左右。岂非攘其左右手之谓乎。此说似然。而但与集传不同。未知如何。
是攘臂而就也。吕东莱云攘之者。喜之甚取之疾。而不自知其手之捷狎。然则非不可矣。古文左右皆从手。故少仪曰。居之于左。以左为左手矣。檀弓曰。拱而尚右。以右为右手矣。礼仪乡射曰。左右抚矢而乘之。以左右为左右手矣。据此则攘其左右。岂非攘其左右手之谓乎。此说似然。而但与集传不同。未知如何。臣对曰。左右之谓左右手。据少仪,檀弓,乡射等文而观之则似亦如是说得。而大抵观诗之法。不必泥看于字句。盖此田畯至喜之际。欲尝其馌之旨否。而迭取左右之人。可见其亲爱之无间于彼此。而以手攘取之义。自在里许。恐当以集传所释为正矣。
大田
御制条问曰。秉畀炎火。以姚崇事观之。是人为也。非神为也。而诗人之言。乃请于田祖。何也。田祖而有神。则初令四虫不生可也。或使四虫自死可也。而持而投诸火中则不能也。然则请于田祖者。盖将以人力投火而愿神之助之也。犹言神假手于人尔。如是看为好欤。
臣对曰。四虫之生。初因阳盛而气赢。则乘气化生之理。固非田神之可令不生也。既乘气赢而生者。苟非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7H 页
 气缩。亦无自消之理。则又非田神之或使自死也。惟其可为者。必用人力消灭。而是则田祖之神不无可助之道。故谓将投诸炎火而愿神之有助也。集传姚崇事盖亦此类。而犹言神假手于人。诚如 圣教。
气缩。亦无自消之理。则又非田神之或使自死也。惟其可为者。必用人力消灭。而是则田祖之神不无可助之道。故谓将投诸炎火而愿神之有助也。集传姚崇事盖亦此类。而犹言神假手于人。诚如 圣教。瞻彼洛矣
御制条问曰。福禄如茨。注曰。茨。积也。按甫田章。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注曰。茨。屋盖。言其密比也。此章所云如茨。亦只是言屋茨之茨。实言福禄之多如屋茨之密比也。而注不以屋盖解茨。而以积为训。何欤。
臣对曰。诗之一字两用。如遹字。小旻则作辟。文王有声则作聿。如濯字。灵台则作肥泽。文王有声则作大。若此类者固多。而要皆随其辞而意各不同。今此如茨之茨。本是屋盖之名。而甫田则直以屋盖释之。此章则以积也释之者。彼盖喻积稼之状。故取譬于屋盖。此则泛言福禄之盛。故只取其积之义也。若楚茨之茨。又是蒺藜之名而与此绝异。盖所取之义各殊。故所释之言。亦从而不同也。
御制条问曰。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而此诗只以讲武事为万年保邦之道。何欤。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武事是讲。则其必先有文事可知故欤。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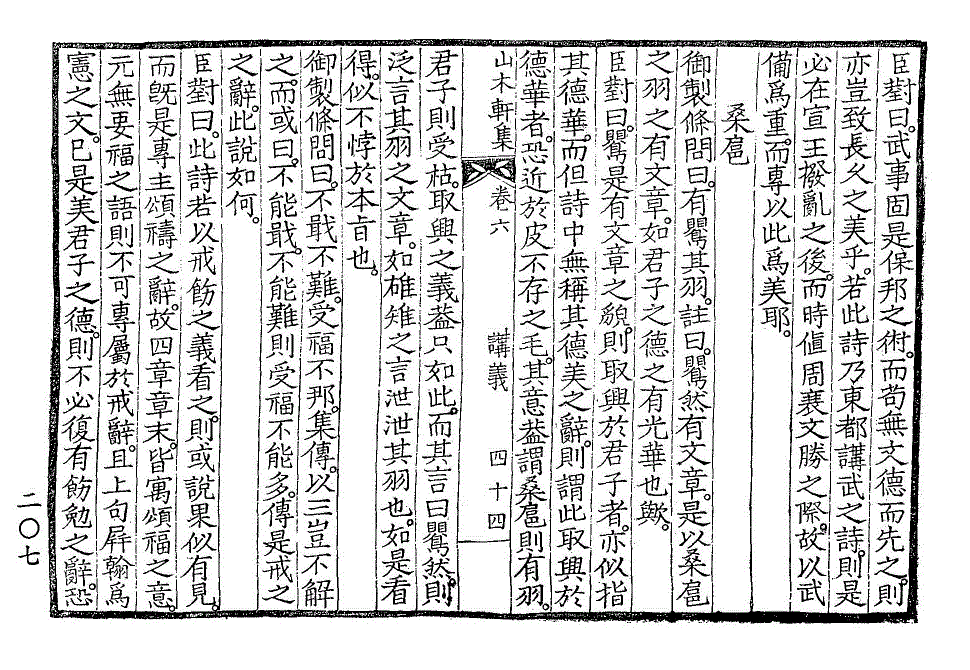 臣对曰。武事固是保邦之术。而苟无文德而先之。则亦岂致长久之美乎。若此诗乃东都讲武之诗。则是必在宣王拨乱之后。而时值周衰文胜之际。故以武备为重。而专以此为美耶。
臣对曰。武事固是保邦之术。而苟无文德而先之。则亦岂致长久之美乎。若此诗乃东都讲武之诗。则是必在宣王拨乱之后。而时值周衰文胜之际。故以武备为重。而专以此为美耶。桑扈
御制条问曰。有莺其羽。注曰。莺然有文章。是以桑扈之羽之有文章。如君子之德之有光华也欤。
臣对曰。莺是有文章之貌。则取兴于君子者。亦似指其德华。而但诗中无称其德美之辞。则谓此取兴于德华者。恐近于皮不存之毛。其意盖谓桑扈则有羽。君子则受祜。取兴之义盖只如此。而其言曰莺然。则泛言其羽之文章。如雄雉之言泄泄其羽也。如是看得。似不悖于本旨也。
御制条问曰。不戢不难。受福不那。集传。以三岂不解之。而或曰。不能戢。不能难则受福不能多。传是戒之之辞。此说如何。
臣对曰。此诗若以戒饬之义看之。则或说果似有见。而既是专主颂祷之辞。故四章章末。皆寓颂福之意。元无要福之语则不可专属于戒辞。且上句屏翰为宪之文。已是美君子之德。则不必复有饬勉之辞。恐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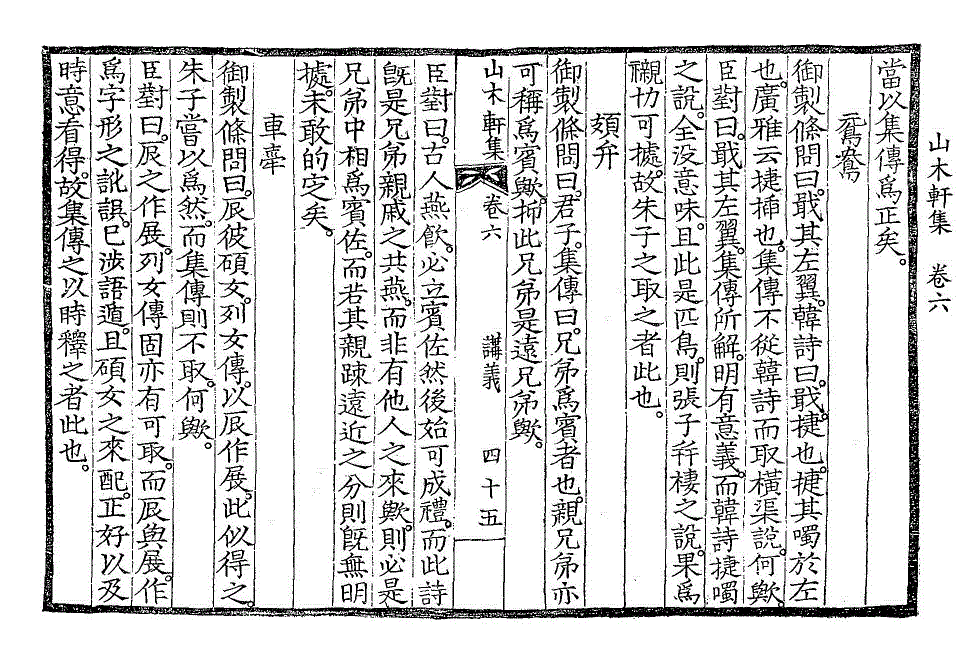 当以集传为正矣。
当以集传为正矣。䲶鸯
御制条问曰。戢其左翼。韩诗曰。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广雅云捷插也。集传不从韩诗而取横渠说。何欤。
臣对曰。戢其左翼。集传所解。明有意义。而韩诗捷噣之说。全没意味。且此是匹鸟。则张子并栖之说。果为衬切可据。故朱子之取之者此也。
頍弁
御制条问曰。君子。集传曰。兄弟为宾者也。亲兄弟亦可称为宾欤。抑此兄弟是远兄弟欤。
臣对曰。古人燕饮。必立宾佐然后始可成礼。而此诗既是兄弟亲戚之共燕。而非有他人之来欤。则必是兄弟中相为宾佐。而若其亲疏远近之分则既无明据。未敢的定矣。
车辖
御制条问曰。辰彼硕女。列女传。以辰作展。此似得之。朱子尝以为然。而集传则不取。何欤。
臣对曰。辰之作展。列女传固亦有可取。而辰与展。作为字形之讹误。已涉语遁。且硕女之来配。正好以及时意看得。故集传之以时释之者此也。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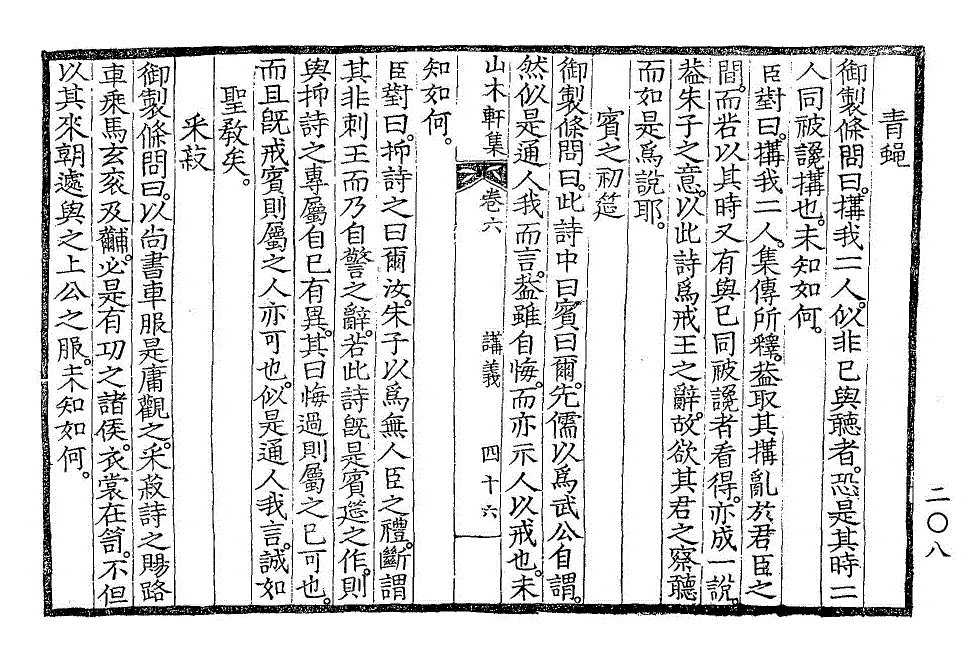 青蝇
青蝇御制条问曰。搆我二人。似非己与听者。恐是其时二人同被谗搆也。未知如何。
臣对曰。搆我二人。集传所释。盖取其搆乱于君臣之间。而若以其时又有与己同被谗者看得。亦成一说。盖朱子之意。以此诗为戒王之辞。故欲其君之察听而如是为说耶。
宾之初筵
御制条问曰。此诗中曰宾曰尔。先儒以为武公自谓。然似是通人我而言。盖虽自悔。而亦示人以戒也。未知如何。
臣对曰。抑诗之曰尔汝。朱子以为无人臣之礼。断谓其非刺王而乃自警之辞。若此诗既是宾筵之作。则与抑诗之专属自己有异。其曰悔过则属之己可也。而且既戒宾则属之人亦可也。似是通人我言。诚如 圣教矣。
采菽
御制条问曰。以尚书车服是庸观之。采菽诗之赐路车乘马玄衮及黼。必是有功之诸侯。衣裳在笥。不但以其来朝遽与之上公之服。未知如何。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9H 页
 臣对曰。车服之赐。果是锡庸之典。如非有功诸侯则不宜轻予。而观于此诗。概无酬绩之语。岂或但以来朝而遽赐之也。若篇中所谓殿天子之邦。是乃美其德之辞。则或以此为命德之章。故嘉其有德而与之者。与锡庸无间耶。
臣对曰。车服之赐。果是锡庸之典。如非有功诸侯则不宜轻予。而观于此诗。概无酬绩之语。岂或但以来朝而遽赐之也。若篇中所谓殿天子之邦。是乃美其德之辞。则或以此为命德之章。故嘉其有德而与之者。与锡庸无间耶。角弓
御制条问曰。骍骍。集传曰。弓调和貌。或曰。骍骍。弓之赤色也。此说何如。
臣对曰。试以彤弓弨兮之意看之。则彤弓是赏功之物也。取以为不亲亲之兴无意义。此集传所以以调和释之也。
都人士
御制条问曰。万民所望之望。似非仰望。而是候望也。盖其人离于故都。故愿见其归于周而候望之也。未知如何。
臣对曰。王都。天下之所视效也。平时犹然。况此周衰之馀。邑都迁改。人物凋残。已非旧日之盛。而无复效法之所。则民之思望而愿见者当如何哉。一有行归之人。其所候望。自是常情之必然。
采绿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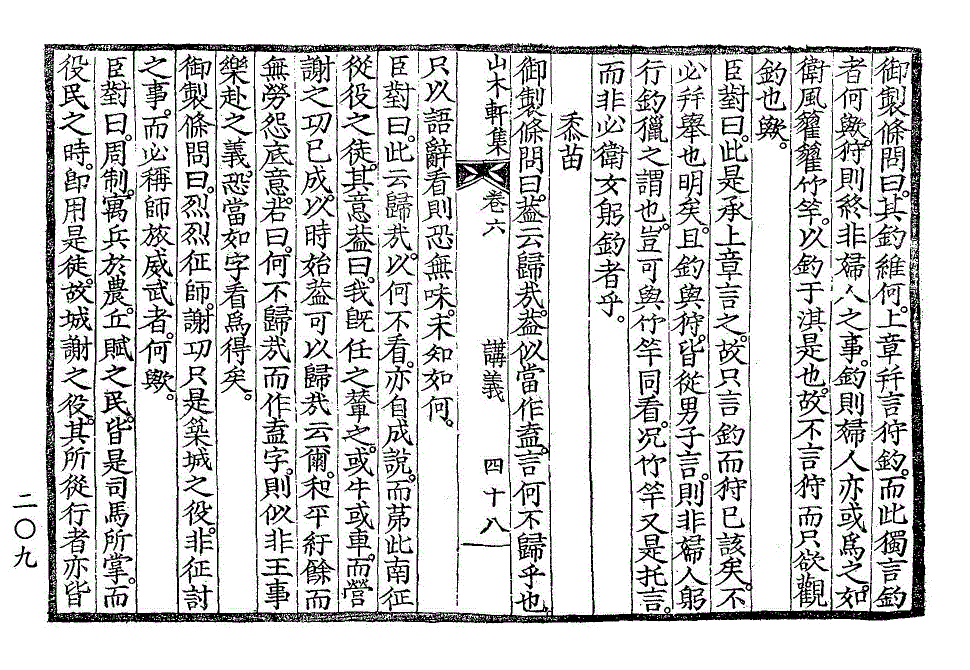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其钓维何。上章并言狩钓。而此独言钓者何欤。狩则终非妇人之事。钓则妇人亦或为之。如卫风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是也。故不言狩而只欲观钓也欤。
御制条问曰。其钓维何。上章并言狩钓。而此独言钓者何欤。狩则终非妇人之事。钓则妇人亦或为之。如卫风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是也。故不言狩而只欲观钓也欤。臣对曰。此是承上章言之。故只言钓而狩已该矣。不必并举也明矣。且钓与狩。皆从男子言。则非妇人躬行钓猎之谓也。岂可与竹竿同看。况竹竿又是托言。而非必卫女躬钓者乎。
黍苗
御制条问曰。盖云归哉。盖似当作盍。言何不归乎也。只以语辞看则恐无味。未知如何。
臣对曰。此云归哉。以何不看。亦自成说。而第此南征从役之徒。其意盖曰。我既任之辇之。或牛或车。而营谢之功已成。以时始盖可以归哉云尔。和平纡馀而无劳怨底意。若曰。何不归哉而作盍字。则似非王事乐赴之义。恐当如字看为得矣。
御制条问曰。烈烈征师。谢功只是筑城之役。非征讨之事。而必称师旅威武者。何欤。
臣对曰。周制。寓兵于农。丘赋之民。皆是司马所掌。而役民之时。即用是徒。故城谢之役。其所从行者亦皆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10H 页
 师旅。则其征师盖以此也。而若其烈烈威武之称。所以见召伯蕫率之善也。
师旅。则其征师盖以此也。而若其烈烈威武之称。所以见召伯蕫率之善也。白华
御制条问曰。此诗与邶风绿衣章相类。庄姜申后同有妇德。今于其两诗而观之。辞气之间。其人之优劣。亦有可言者欤。
臣对曰。此诗伤怨之辞。正如绿衣相类。而其发明嫡妾之分。尤有相近者。今以其意观之。亦固有妇德之可言。而但绿衣则其所取喻。只在于嫡妾尊卑之际。而无斥言直怨之辞。且其自反之语。期如古人处心者。可想其正直端洁。而若此篇则其伤悼王室之意。亦可谓出于忠告。然其词旨太露。殊欠婉曲底意。似不无彼善于此矣。
御制条问曰。滮池北流。集传曰。滮。流貌。或曰。滮。池水名。虽水名而亦以滮流故得名。则其义未始有异也。然而大旨小水微流观之。滮是微流貌。而训释去微字。只曰流貌者。欲令于注与大旨互见而知之欤。
臣对曰。滮之为水。亦以其流而得名。则以滮为流貌者。义未尝不同。而大旨既曰微流小水。则微字虽无所释。观于此而亦可推认。注与大旨欲令互见。诚如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10L 页
 圣教矣。
圣教矣。绵蛮
御制条问曰。命彼后车。谓之载之者。此语不可晓。愿闻其义。
臣对曰。此诗盖是微贱之人不得其所。饥渴困劳。思所托身而作。故以不能前进之意。设比于黄鸟之止阿者。专取于下段后车之义也。大抵有后车而命载者。即在位者所事。则其意盖谓使我不得其所而劳困不行者。是由在位者不见恤而然也。由是言之。其言后车命载者。盖欲得其所之意。而未必要子产乘舆之惠。实亦如冯驩无车之叹。诗经本旨。恐亦如是也。
苕之华
御制条问曰。苕之华。或云诗人自言己之憔悴不如苕华之荣。虽与集传不同。此亦可为一义欤。
臣对曰。苕华取比。专以其虽荣不久之义。观于次章所谓不如无生而亦可知矣。集传所释固好。而或说亦成一义。姑备参考。恐然矣。
御制条问曰。三星在罶。罶中无鱼。以渴泽而渔故欤。非必竭泽而渔。叔季运气衰薄。天地之产。自然不富
山木轩集卷之六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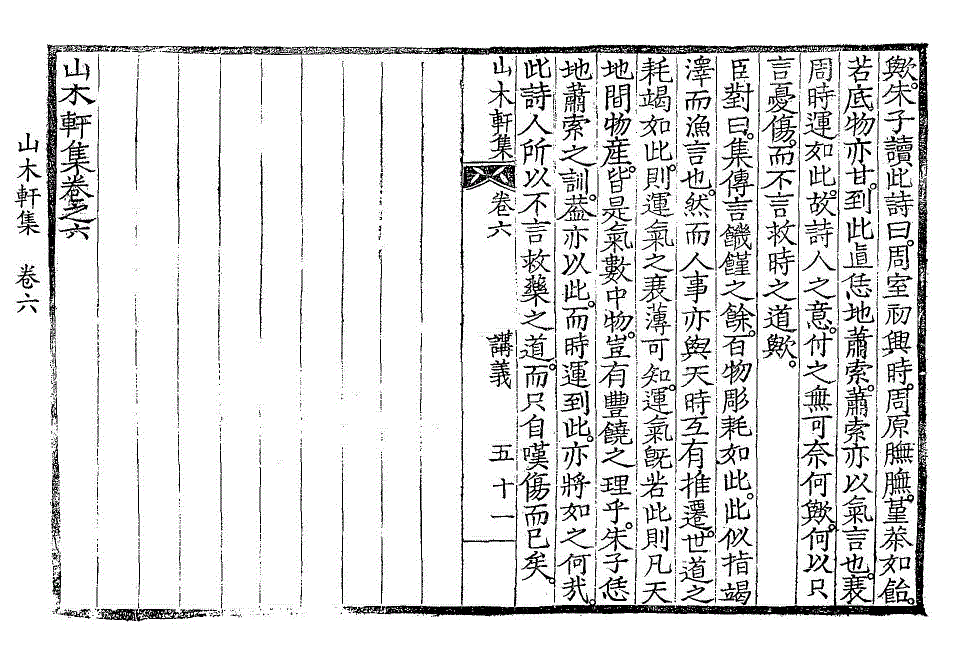 欤。朱子读此诗曰。周室初兴时。周原膴膴。堇茶(一作荼)如饴。若底物亦甘。到此直恁地萧索。萧索亦以气言也。衰周时运如此。故诗人之意。付之无可奈何欤。何以只言忧伤。而不言救时之道欤。
欤。朱子读此诗曰。周室初兴时。周原膴膴。堇茶(一作荼)如饴。若底物亦甘。到此直恁地萧索。萧索亦以气言也。衰周时运如此。故诗人之意。付之无可奈何欤。何以只言忧伤。而不言救时之道欤。臣对曰。集传言饥馑之馀。百物彫耗如此。此似指竭泽而渔言也。然而人事亦与天时互有推迁。世道之耗竭如此。则运气之衰薄可知。运气既若此则凡天地间物产。皆是气数中物。岂有丰饶之理乎。朱子恁地萧索之训。盖亦以此。而时运到此。亦将如之何哉。此诗人所以不言救药之道。而只自叹伤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