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x 页
山木轩集卷之五
讲义
讲义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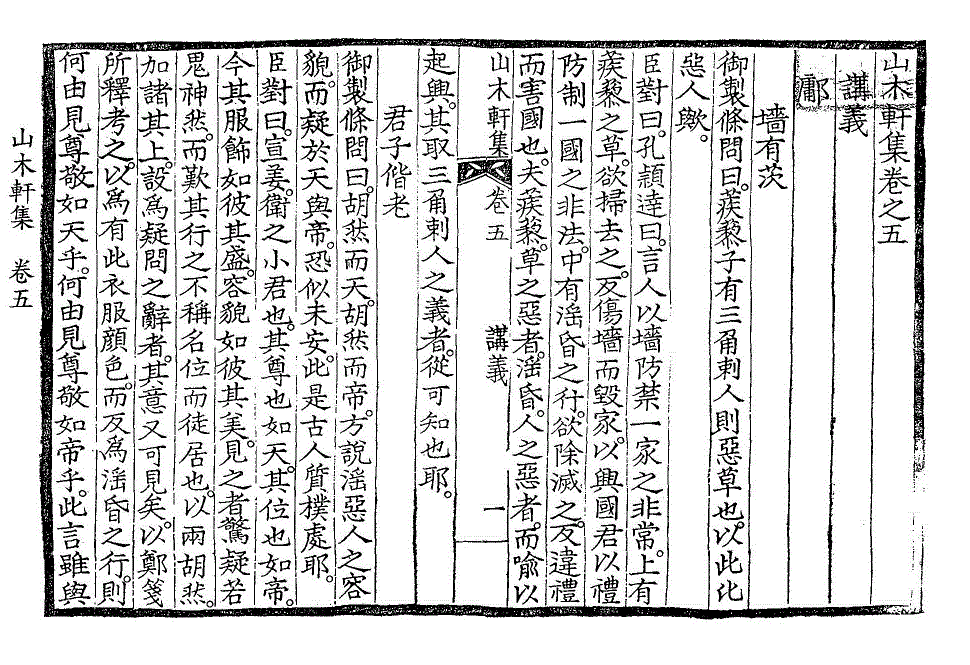 鄘
鄘墙有茨
御制条问曰。蒺藜子有三角刺人则恶草也。以此比恶人欤。
臣对曰。孔颖达曰。言人以墙防禁一家之非常。上有蒺藜之草。欲扫去之。反伤墙而毁家。以兴国君以礼防制一国之非法。中有淫昏之行。欲除灭之。反违礼而害国也。夫蒺藜。草之恶者。淫昏。人之恶者。而喻以起兴。其取三角刺人之义者。从可知也耶。
君子偕老
御制条问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方说淫恶人之容貌。而疑于天与帝。恐似未安。此是古人质朴处耶。
臣对曰。宣姜。卫之小君也。其尊也如天。其位也如帝。今其服饰如彼其盛。容貌如彼其美。见之者惊疑若鬼神然。而叹其行之不称名位而徒居也。以两胡然。加诸其上。设为疑问之辞者。其意又可见矣。以郑笺所释考之。以为有此衣服颜色。而反为淫昏之行。则何由见尊敬如天乎。何由见尊敬如帝乎。此言虽与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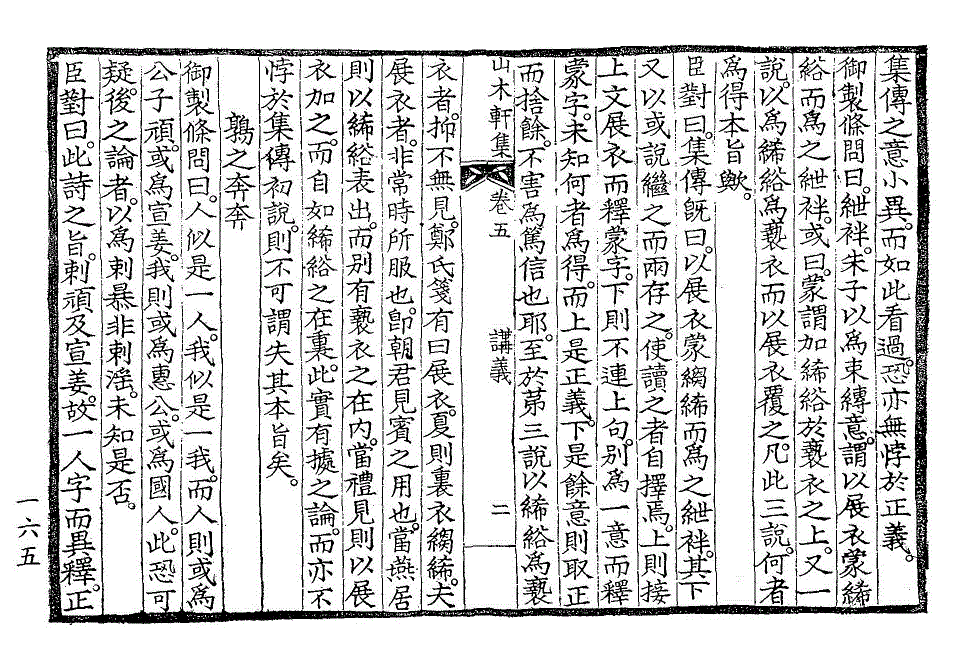 集传之意小异。而如此看过。恐亦无悖于正义。
集传之意小异。而如此看过。恐亦无悖于正义。御制条问曰。绁袢。朱子以为束缚意。谓以展衣蒙絺绤而为之绁袢。或曰。蒙谓加絺绤于亵衣之上。又一说。以为絺绤为亵衣而以展衣覆之。凡此三说。何者为得本旨欤。
臣对曰。集传既曰。以展衣蒙绉絺而为之绁袢。其下又以或说继之而两存之。使读之者自择焉。上则接上文展衣而释蒙字。下则不连上句。别为一意而释蒙字。未知何者为得。而上是正义。下是馀意则取正而舍馀。不害为笃信也耶。至于第三说以絺绤为亵衣者。抑不无见。郑氏笺有曰展衣。夏则里衣绉絺。夫展衣者。非常时所服也。即朝君见宾之用也。当燕居则以絺绤表出。而别有亵衣之在内。当礼见则以展衣加之。而自如絺绤之在里。此实有据之论。而亦不悖于集传初说。则不可谓失其本旨矣。
鹑之奔奔
御制条问曰。人似是一人。我似是一我。而人则或为公子顽。或为宣姜。我则或为惠公。或为国人。此恐可疑。后之论者。以为刺暴非刺淫。未知是否。
臣对曰。此诗之旨。刺顽及宣姜。故一人字而异释。正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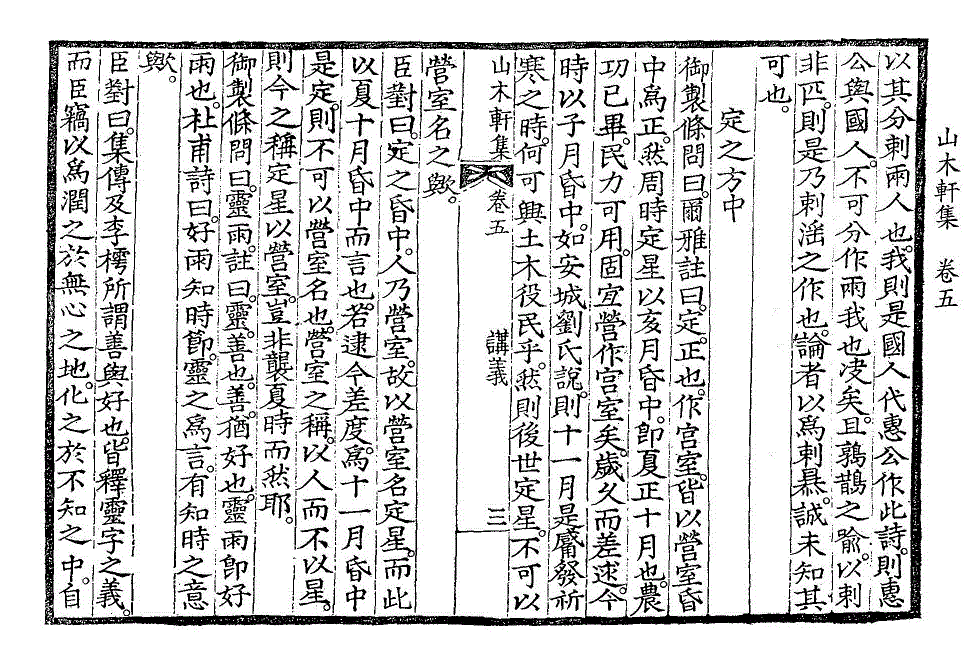 以其分刺两人也。我则是国人代惠公作此诗。则惠公与国人。不可分作两我也决矣。且鹑鹊之喻。以刺非匹。则是乃刺淫之作也。论者以为刺暴。诚未知其可也。
以其分刺两人也。我则是国人代惠公作此诗。则惠公与国人。不可分作两我也决矣。且鹑鹊之喻。以刺非匹。则是乃刺淫之作也。论者以为刺暴。诚未知其可也。定之方中
御制条问曰。尔雅注曰。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昏中为正。然周时定星以亥月昏中。即夏正十月也。农功已毕。民力可用。固宜营作宫室矣。岁久而差逑。今时以子月昏中。如安城刘氏说。则十一月是觱发祈寒之时。何可兴土木役民乎。然则后世定星。不可以营室名之欤。
臣对曰。定之昏中。人乃营室。故以营室名定星。而此以夏十月昏中而言也。若逮今差度。为十一月昏中是定。则不可以营室名也。营室之称。以人而不以星。则今之称定星以营室。岂非袭夏时而然耶。
御制条问曰。灵雨。注曰。灵。善也。善。犹好也。灵雨即好雨也。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灵之为言。有知时之意欤。
臣对曰。集传及李樗所谓善与好也。皆释灵字之义。而臣窃以为润之于无心之地。化之于不知之中。自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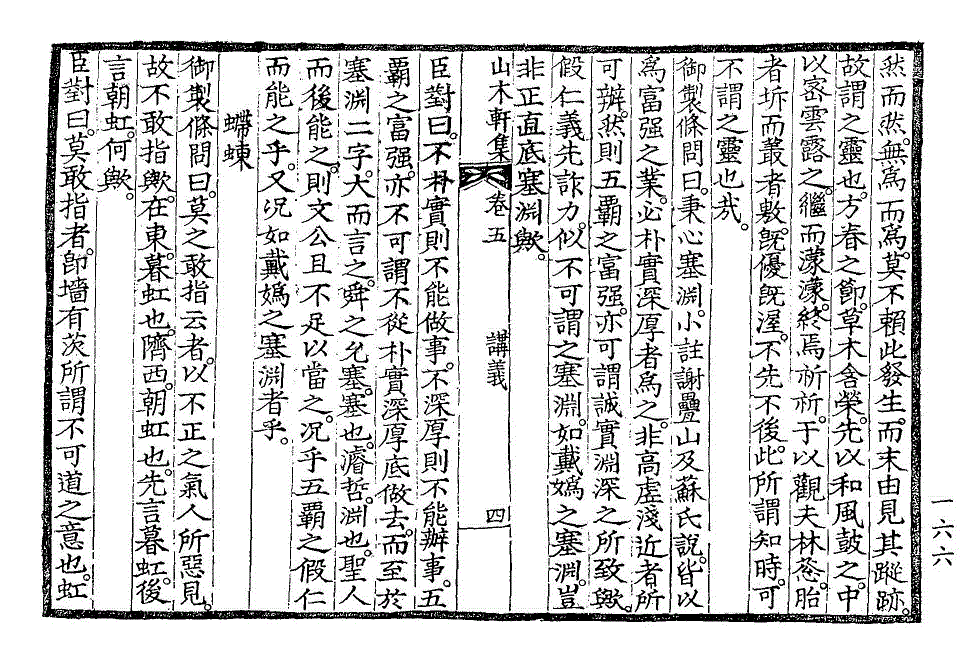 然而然。无为而为。莫不赖此发生。而末由见其踪迹。故谓之灵也。方春之节。草木含荣。先以和风鼓之。中以密云露之。继而濛濛。终焉祈祈。于以观夫林葱。胎者坼而丛者敷。既优既渥。不先不后。此所谓知时。可不谓之灵也哉。
然而然。无为而为。莫不赖此发生。而末由见其踪迹。故谓之灵也。方春之节。草木含荣。先以和风鼓之。中以密云露之。继而濛濛。终焉祈祈。于以观夫林葱。胎者坼而丛者敷。既优既渥。不先不后。此所谓知时。可不谓之灵也哉。御制条问曰。秉心塞渊。小注谢叠山及苏氏说。皆以为富强之业。必朴实深厚者为之。非高虚浅近者所可办。然则五霸之富强。亦可谓诚实渊深之所致欤。假仁义先诈力。似不可谓之塞渊。如戴妫之塞渊。岂非正直底塞渊欤。
臣对曰。不朴实则不能做事。不深厚则不能办事。五霸之富强。亦不可谓不从朴实深厚底做去。而至于塞渊二字。大而言之。舜之允塞。塞也。浚哲。渊也。圣人而后能之。则文公且不足以当之。况乎五霸之假仁而能之乎。又况如戴妫之塞渊者乎。
螮蝀
御制条问曰。莫之敢指云者。以不正之气人所恶见。故不敢指欤。在东。暮虹也。隮西。朝虹也。先言暮虹。后言朝虹。何欤。
臣对曰。莫敢指者。即墙有茨所谓不可道之意也。虹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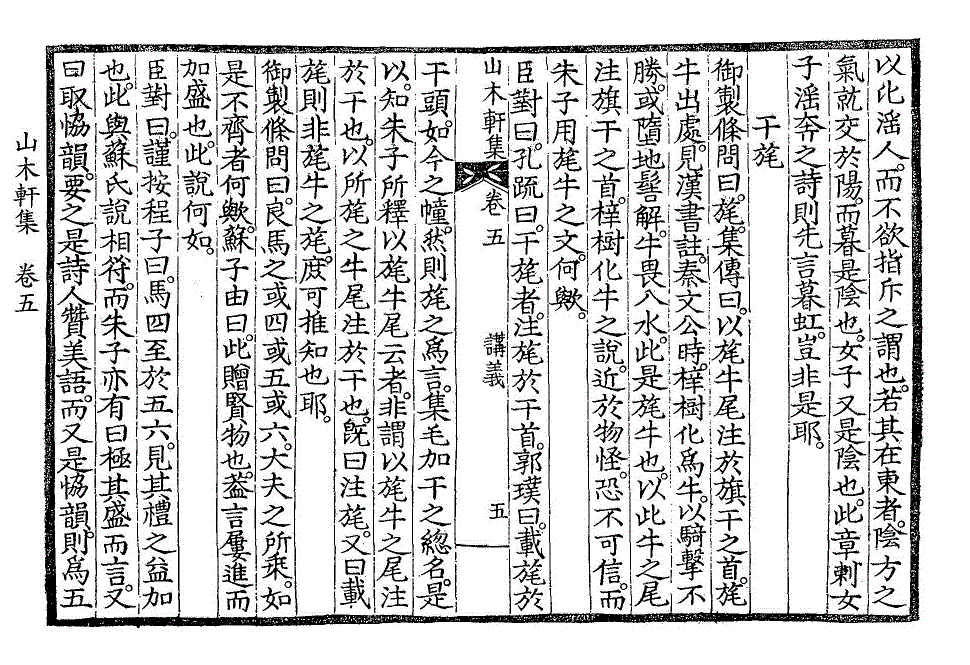 以比淫人。而不欲指斥之谓也。若其在东者。阴方之气就交于阳。而暮是阴也。女子又是阴也。此章刺女子淫奔之诗则先言暮虹。岂非是耶。
以比淫人。而不欲指斥之谓也。若其在东者。阴方之气就交于阳。而暮是阴也。女子又是阴也。此章刺女子淫奔之诗则先言暮虹。岂非是耶。干旄
御制条问曰。旄。集传曰。以旄牛尾注于旗干之首。旄牛出处。见汉书注。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不胜。或堕地髻解。牛畏入水。此是旄牛也。以此牛之尾注旗干之首。梓树化牛之说。近于物怪。恐不可信。而朱子用旄牛之文。何欤。
臣对曰。孔疏曰。干旄者。注旄于干首。郭璞曰。载旄于干头。如今之幢。然则旄之为言。集毛加干之总名。是以。知朱子所释以旄牛尾云者。非谓以旄牛之尾注于干也。以所旄之牛尾注于干也。既曰注旄。又曰载旄则非旄牛之旄。庶可推知也耶。
御制条问曰。良马之或四或五或六。大夫之所乘。如是不齐者何欤。苏子由曰。此赠贤物也。盖言屡进而加盛也。此说何如。
臣对曰。谨按程子曰。马四至于五六。见其礼之益加也。此与苏氏说相符。而朱子亦有曰极其盛而言。又曰取协韵。要之是诗人赞美语。而又是协韵。则为五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7L 页
 为六。恐无深意。
为六。恐无深意。载驰
御制条问曰。控于大邦。盖欲赴愬而托归唁耳。妇人既不可自为赴愬。则何不以此请于穆公。遣使告方伯。救卫之亡。而有谁因谁极之语欤。婚媾相恤之义。举废国之道。在穆公。岂有不可欤。
臣对曰。𧟄(一作壤)地褊小。无以自振。军民凋弊。无以相救。况当春秋搂伐之时。安能以许之力。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为兴灭继绝之图耶。以诗意考之。不全在于托控愬而欲归唁也。尽亦有真个悼伤其无可因极之意。严粲所谓托归唁为词者。恐失集传之本旨也耶。
卫
淇奥
御制条问曰。淇奥。或以为二水名。引博物志有奥水流入于淇。水经。肥水谓之澳之文。以澳作奥。而此未必然。汉书既云伐竹于淇。则淇是有竹之处。未闻奥水亦有竹也。且尔雅曰。厓内为奥。今不信尔雅之文。而信博物志之文。未知其可也。如何。
臣对曰。卫之国。以河为境。国内之水无大于淇。而凡卫诗之称淇。不啻屡见。有如亦流于淇。送我乎淇。以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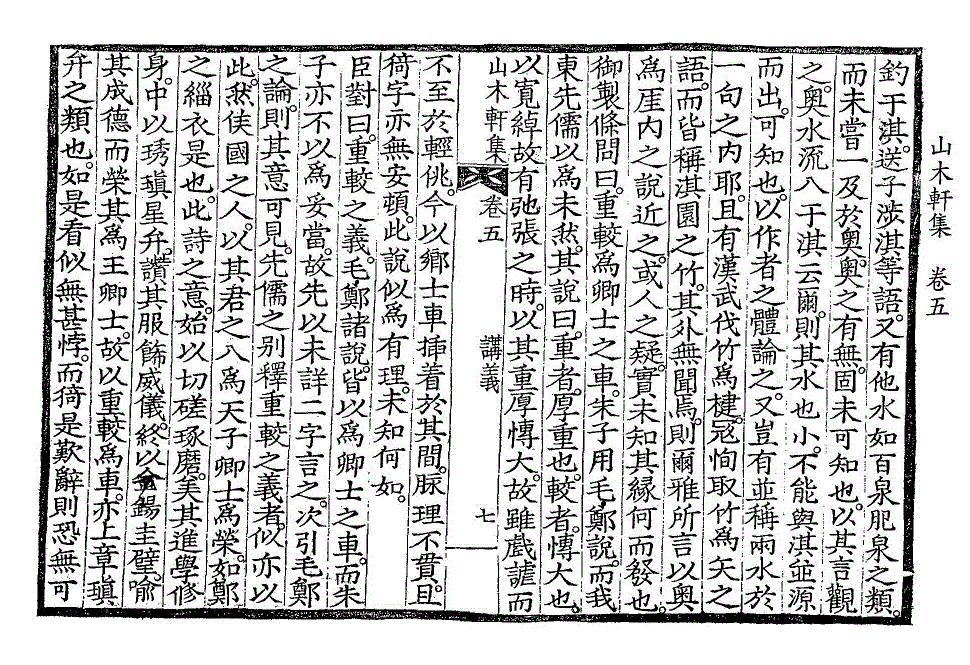 钓于淇。送子涉淇等语。又有他水如百泉肥泉之类。而未尝一及于奥。奥之有无。固未可知也。以其言观之。奥水流入于淇云尔。则其水也小。不能与淇并源而出。可知也。以作者之体论之。又岂有并称两水于一句之内耶。且有汉武伐竹为楗。寇恂取竹为矢之语。而皆称淇园之竹。其外无闻焉。则尔雅所言以奥为厓内之说近之。或人之疑。实未知其缘何而发也。
钓于淇。送子涉淇等语。又有他水如百泉肥泉之类。而未尝一及于奥。奥之有无。固未可知也。以其言观之。奥水流入于淇云尔。则其水也小。不能与淇并源而出。可知也。以作者之体论之。又岂有并称两水于一句之内耶。且有汉武伐竹为楗。寇恂取竹为矢之语。而皆称淇园之竹。其外无闻焉。则尔雅所言以奥为厓内之说近之。或人之疑。实未知其缘何而发也。御制条问曰。重较为卿士之车。朱子用毛,郑说。而我东先儒以为未然。其说曰。重者。厚重也。较者。博大也。以宽绰故有弛张之时。以其重厚博大。故虽戏谑而不至于轻佻。今以乡士车插着于其间。脉理不贯。且猗字亦无安顿。此说似为有理。未知何如。
臣对曰。重较之义。毛,郑诸说。皆以为卿士之车。而朱子亦不以为妥当。故先以未详二字言之。次引毛,郑之论。则其意可见。先儒之别释重较之义者。似亦以此。然侯国之人。以其君之入为天子卿士为荣。如郑之缁衣是也。此诗之意。始以切磋琢磨。美其进学修身。中以琇瑱星弁。赞其服饰威仪。终以金锡圭璧。喻其成德而荣其为王卿士。故以重较为车。亦上章瑱弁之类也。如是看似无甚悖。而猗是叹辞则恐无可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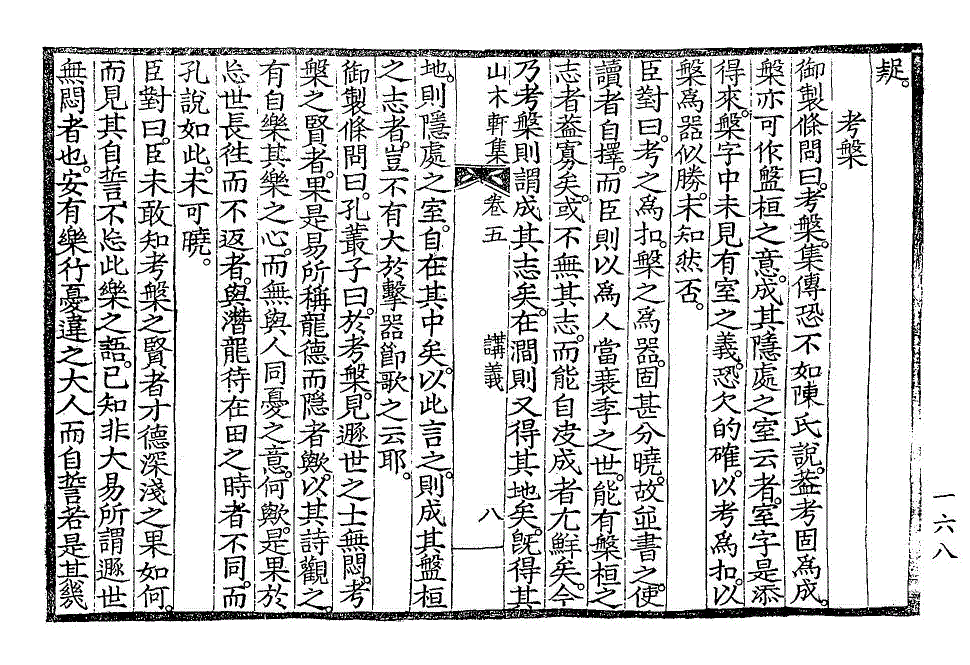 疑。
疑。考槃
御制条问曰。考槃。集传恐不如陈氏说。盖考固为成。槃亦可作盘桓之意。成其隐处之室云者。室字是添得来。槃字中未见有室之义。恐欠的确。以考为扣。以槃为器似胜。未知然否。
臣对曰。考之为扣。槃之为器。固甚分晓。故并书之。使读者自择。而臣则以为人当衰季之世。能有槃桓之志者盖寡矣。或不无其志。而能自决成者尤鲜矣。今乃考槃则谓成其志矣。在涧则又得其地矣。既得其地。则隐处之室。自在其中矣。以此言之。则成其盘桓之志者。岂不有大于击器节歌之云耶。
御制条问曰。孔丛子曰。于考槃。见遁世之士无闷。考槃之贤者。果是易所称龙德而隐者欤。以其诗观之。有自乐其乐之心。而无与人同忧之意。何欤。是果于忘世长往而不返者。与潜龙待在田之时者不同。而孔说如此。未可晓。
臣对曰。臣未敢知考槃之贤者才德深浅之果如何。而见其自誓不忘此乐之语。已知非大易所谓遁世无闷者也。安有乐行忧违之大人而自誓若是其几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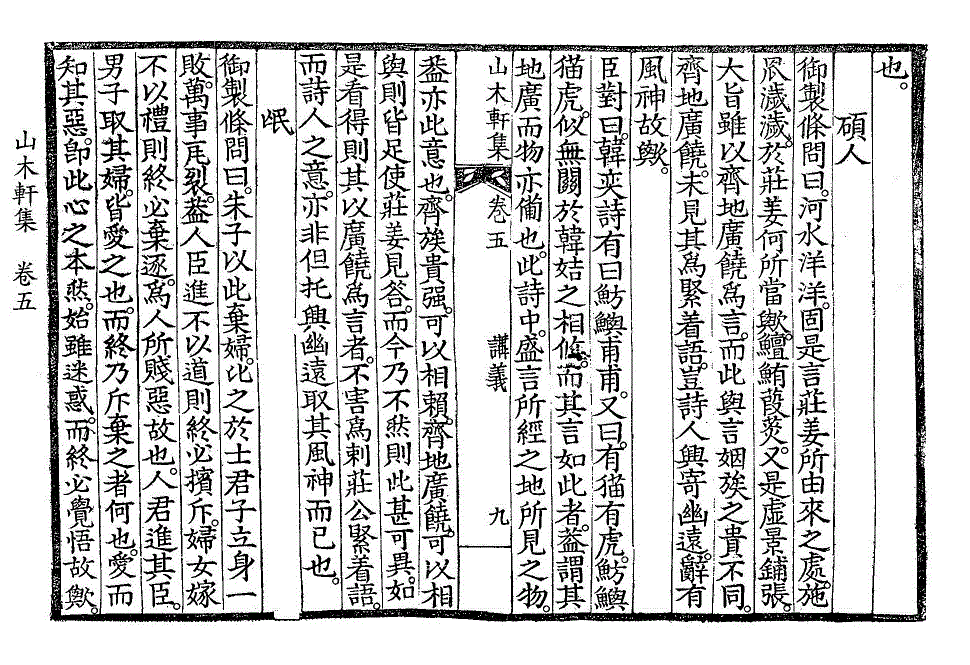 也。
也。硕人
御制条问曰。河水洋洋。固是言庄姜所由来之处。施罛濊濊。于庄姜何所当欤。鳣鲔葭菼。又是虚景铺张。大旨虽以齐地广饶为言。而此与言姻族之贵不同。齐地广饶。未见其为紧着语。岂诗人兴寄幽远。辞有风神故欤。
臣对曰。韩奕诗有曰鲂鱮甫甫。又曰。有猫有虎。鲂鱮猫虎。似无关于韩姞之相攸。而其言如此者。盖谓其地广而物亦备也。此诗中。盛言所经之地所见之物。盖亦此意也。齐族贵强。可以相赖。齐地广饶。可以相与则皆足使庄姜见答。而今乃不然则此甚可异。如是看得则其以广饶为言者。不害为刺庄公紧着语。而诗人之意。亦非但托兴幽远取其风神而已也。
氓
御制条问曰。朱子以此弃妇。比之于士君子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盖人臣进不以道则终必摈斥。妇女嫁不以礼则终必弃逐。为人所贱恶故也。人君进其臣。男子取其妇。皆爱之也。而终乃斥弃之者何也。爱而知其恶。即此心之本然。始虽迷惑。而终必觉悟故欤。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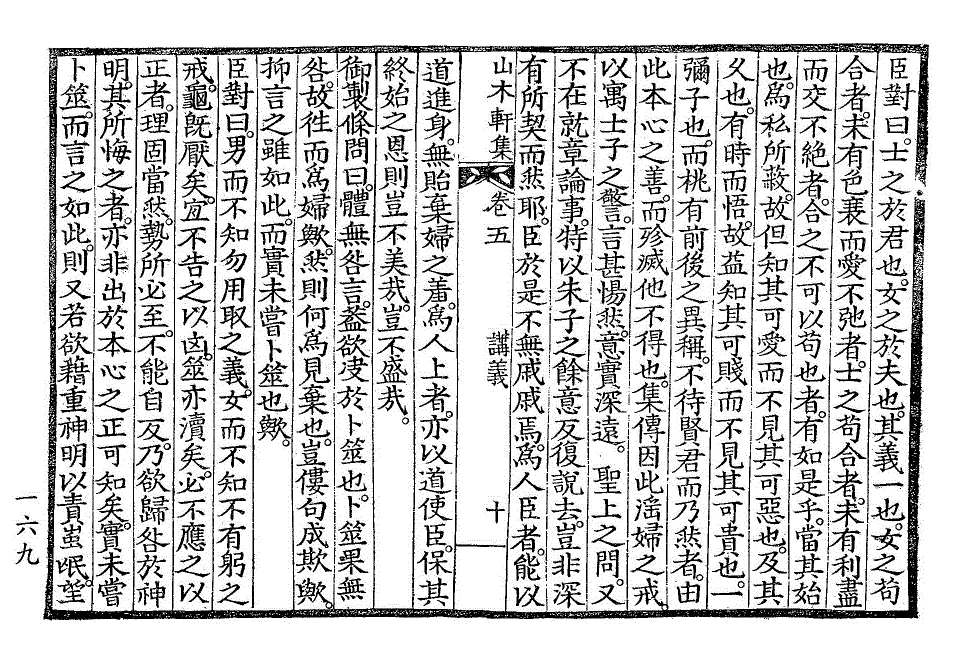 臣对曰。士之于君也。女之于夫也。其义一也。女之苟合者。未有色衰而爱不弛者。士之苟合者。未有利尽而交不绝者。合之不可以苟也者。有如是乎。当其始也。为私所蔽。故但知其可爱而不见其可恶也。及其久也。有时而悟。故益知其可贱而不见其可贵也。一弥子也。而桃有前后之异称。不待贤君而乃然者。由此本心之善。而殄灭他不得也。集传因此淫妇之戒。以寓士子之警。言甚惕然。意实深远。 圣上之问。又不在就章论事。特以朱子之馀意反复说去。岂非深有所契而然耶。臣于是不无戚戚焉。为人臣者。能以道进身。无贻弃妇之羞。为人上者。亦以道使臣。保其终始之恩则岂不美哉。岂不盛哉。
臣对曰。士之于君也。女之于夫也。其义一也。女之苟合者。未有色衰而爱不弛者。士之苟合者。未有利尽而交不绝者。合之不可以苟也者。有如是乎。当其始也。为私所蔽。故但知其可爱而不见其可恶也。及其久也。有时而悟。故益知其可贱而不见其可贵也。一弥子也。而桃有前后之异称。不待贤君而乃然者。由此本心之善。而殄灭他不得也。集传因此淫妇之戒。以寓士子之警。言甚惕然。意实深远。 圣上之问。又不在就章论事。特以朱子之馀意反复说去。岂非深有所契而然耶。臣于是不无戚戚焉。为人臣者。能以道进身。无贻弃妇之羞。为人上者。亦以道使臣。保其终始之恩则岂不美哉。岂不盛哉。御制条问曰。体无咎言。盖欲决于卜筮也。卜筮果无咎。故往而为妇欤。然则何为见弃也。岂偻句成欺欤。抑言之虽如此。而实未尝卜筮也欤。
臣对曰。男而不知勿用取之义。女而不知不有躬之戒。龟既厌矣。宜不告之以凶。筮亦渎矣。必不应之以正者。理固当然。势所必至。不能自反。乃欲归咎于神明。其所悔之者。亦非出于本心之正可知矣。实未尝卜筮。而言之如此。则又若欲藉重神明以责蚩氓。望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0H 页
 其回心。其计益巧憯。安知其必不然。而诬其神明。又当如何哉。
其回心。其计益巧憯。安知其必不然。而诬其神明。又当如何哉。竹竿
御制条问曰。巧笑之𤧳(一作瑳)。佩玉之傩。似是道前时事。盖言未嫁时言笑游戏于二水之间。而叹今之不能然也。如是看颇似有味。而大旨无此意思。未知如何。
臣对曰。既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则其未嫁之时。言笑游嬉于其上之意。已具足矣。其下文即曰。今何由而巧笑于此地乎。又何由而佩玉于此地乎。如此然后语有次序。文有曲折。若以四句皆属于未嫁时事。则意味或反不足也耶。大旨中自恨其不得云云。似道出此个意。
河广
御制条问曰。宋襄公即位。在于卫南渡后。则不隔河矣。何以谓河广。我东先儒以为兴体。此似可通欤。
臣对曰。此诗臣窃尝疑之。若谓宋襄即位后。则果非隔河之地也。此严氏所以以旧说为误者也。若谓桓公尚在时。则安有己出而思其复往乎。此朱子所以从旧说而释之者也。两说皆有窒碍处。以文体论之。东儒之说。诚亦有见也耶。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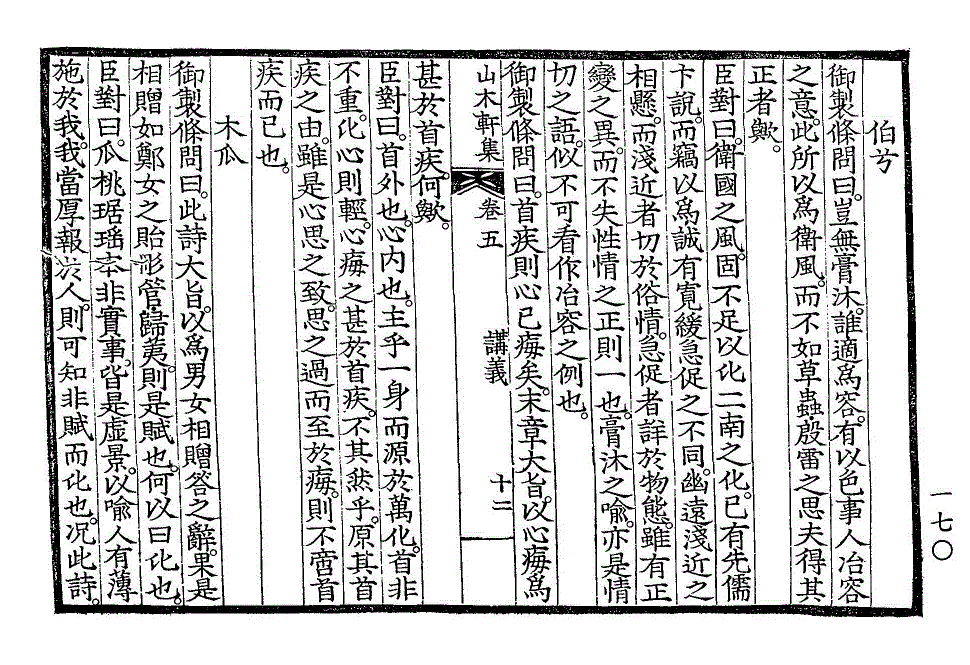 伯兮
伯兮御制条问曰。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有以色事人冶容之意。此所以为卫风。而不如草虫,殷雷之思夫得其正者欤。
臣对曰。卫国之风。固不足以比二南之化。已有先儒卞说。而窃以为诚有宽缓急促之不同。幽远浅近之相悬。而浅近者切于俗情。急促者详于物态。虽有正变之异。而不失性情之正则一也。膏沐之喻。亦是情切之语。似不可看作冶容之例也。
御制条问曰。首疾则心已痗矣。末章大旨。以心痗为甚于首疾。何欤。
臣对曰。首外也。心内也。主乎一身而源于万化。首非不重。比心则轻。心痗之甚于首疾。不其然乎。原其首疾之由。虽是心思之致。思之过而至于痗。则不啻首疾而已也。
木瓜
御制条问曰。此诗大旨。以为男女相赠答之辞。果是相赠如郑女之贻彤管,归荑。则是赋也。何以曰比也。
臣对曰。瓜桃琚瑶本非实事。皆是虚景。以喻人有薄施于我。我当厚报于人。则可知非赋而比也。况此诗。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1H 页
 以郑笺观之。卫人美齐桓之辞也。其义尤较如矣。朱子虽不取。而大旨亦以疑亦二字加之男女之上。非断辞也。安知郑说之必不然乎。
以郑笺观之。卫人美齐桓之辞也。其义尤较如矣。朱子虽不取。而大旨亦以疑亦二字加之男女之上。非断辞也。安知郑说之必不然乎。王
黍离
御制条问曰。此诗第二章注。言稷下垂如心之醉。第三章注。言稷之实如心之噎。首章稷之苗。不言如心之摇摇。以稷苗之与心摇无所同故耶。或曰。苗之受风而动。如心之摇摇。此说何如。
臣对曰。曰苗曰穗曰实。记其三见之异。而初见则其感也犹浅。再见三见则感之也愈甚。是故。初见则不言如字。再三见则辄下如字。此岂但心之摇摇与苗不同而然耶。乃若或说之强引风动。谓之如心者。凿也。
扬之水
御制条问曰。扬水似是言王室之微弱如水之柔弱。以此意看。则为兴而比欤。
臣对曰。观夫扬之一字。益见其可流而不流之意。比之王室。可谓衬贴。欧阳脩,苏辙亦皆如是看得。是谓兴中之比也。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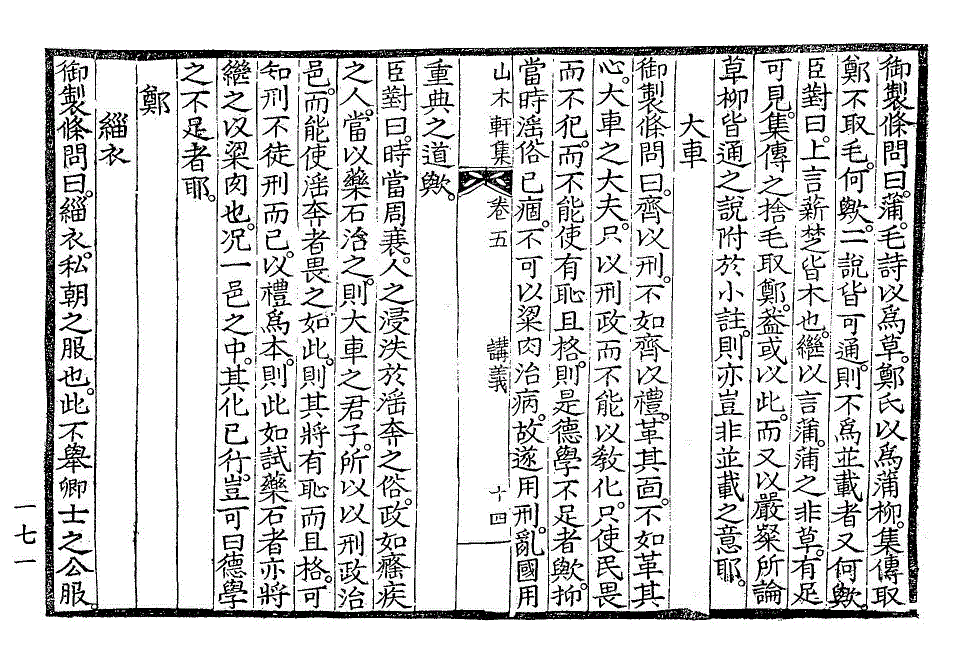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蒲。毛诗以为草。郑氏以为蒲柳。集传取郑不取毛。何欤。二说皆可通。则不为并载者又何欤。
御制条问曰。蒲。毛诗以为草。郑氏以为蒲柳。集传取郑不取毛。何欤。二说皆可通。则不为并载者又何欤。臣对曰。上言薪楚皆木也。继以言蒲。蒲之非草。有足可见。集传之舍毛取郑。盖或以此。而又以严粲所论草柳皆通之说附于小注。则亦岂非并载之意耶。
大车
御制条问曰。齐以刑。不如齐以礼。革其面。不如革其心。大车之大夫。只以刑政而不能以教化。只使民畏而不犯。而不能使有耻且格。则是德学不足者欤。抑当时淫俗已痼。不可以粱肉治病。故遂用刑。乱国用重典之道欤。
臣对曰。时当周衰。人之浸泆于淫奔之俗。政如癃疾之人。当以药石治之。则大车之君子。所以以刑政治邑。而能使淫奔者畏之如此。则其将有耻而且格。可知刑不徒刑而已。以礼为本。则此如试药石者亦将继之以粱肉也。况一邑之中。其化已行。岂可曰德学之不足者耶。
郑
缁衣
御制条问曰。缁衣。私朝之服也。此不举卿士之公服。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2H 页
 而特言私朝之服何欤。私朝之服。每日听政。着之易弊故欤。
而特言私朝之服何欤。私朝之服。每日听政。着之易弊故欤。臣对曰。周人之爱郑公。若郑人之爱其君。故爱之笃而及其私。此所以不言公朝所共见之服而言其私邸之所着者也。若其缁衣之为服。非华采之衣。而既言其弊又改为者。乃所以昭其俭也。又欲其久于职也。如曰听政而易弊。则不亦琐细之甚乎。
羔裘
御制条问曰。舍命司直。可谓贤人。羔裘如濡。与召南之素丝五紽无异。郑国衰乱之世。何以有此等人。而时君能用之为大夫。则不能少有助于政治。何欤。岂一薛居州无如王何者欤。
臣对曰。不患无人而患不能用之。不患不用而患任之之不专。然则朝虽有素丝五紽之贤。其如有赤芾三百之讥。何哉。郑之衰乱若是。则虽有此等人。将不用。用亦不专。则无补于政治可知。此正有一居州之叹。而羔裘三章之兴叹也宜矣。
女曰鸡鸣
御制条问曰。女曰鸡鸣。是郑诗中开眼处。然朱子以为使人手舞足蹈。则不但开眼而已。夫鸡鸣警夫。宜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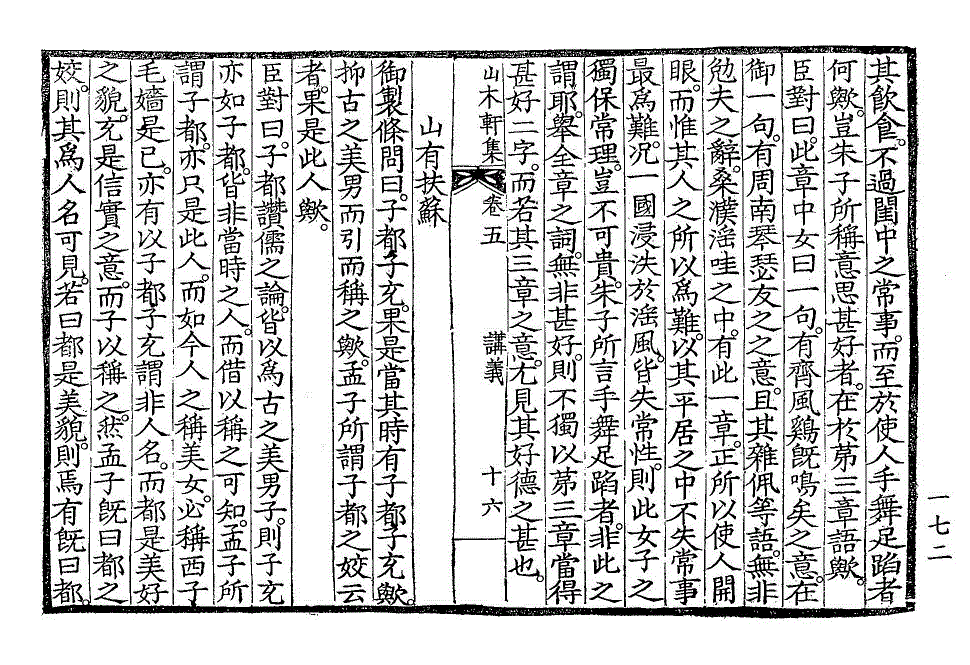 其饮食。不过闺中之常事。而至于使人手舞足蹈者何欤。岂朱子所称意思甚好者。在于第三章语欤。
其饮食。不过闺中之常事。而至于使人手舞足蹈者何欤。岂朱子所称意思甚好者。在于第三章语欤。臣对曰。此章中女曰一句。有齐风鸡既鸣矣之意。在御一句。有周南琴瑟友之之意。且其杂佩等语。无非勉夫之辞。桑濮淫哇之中。有此一章。正所以使人开眼。而惟其人之所以为难。以其平居之中不失常事最为难。况一国浸泆于淫风。皆失常性。则此女子之独保常理。岂不可贵。朱子所言手舞足蹈者。非此之谓耶。举全章之词。无非甚好。则不独以第三章当得甚好二字。而若其三章之意。尤见其好德之甚也。
山有扶苏
御制条问曰。子都,子充。果是当其时有子都,子充欤。抑古之美男而引而称之欤。孟子所谓子都之姣云者。果是此人欤。
臣对曰。子都赞儒之论。皆以为古之美男子。则子充亦如子都。皆非当时之人。而借以称之可知。孟子所谓子都。亦只是此人。而如今人之称美女。必称西子,毛嫱是已。亦有以子都,子充谓非人名。而都是美好之貌。充是信实之意。而子以称之。然孟子既曰都之姣。则其为人名可见。若曰都是美貌。则焉有既曰都。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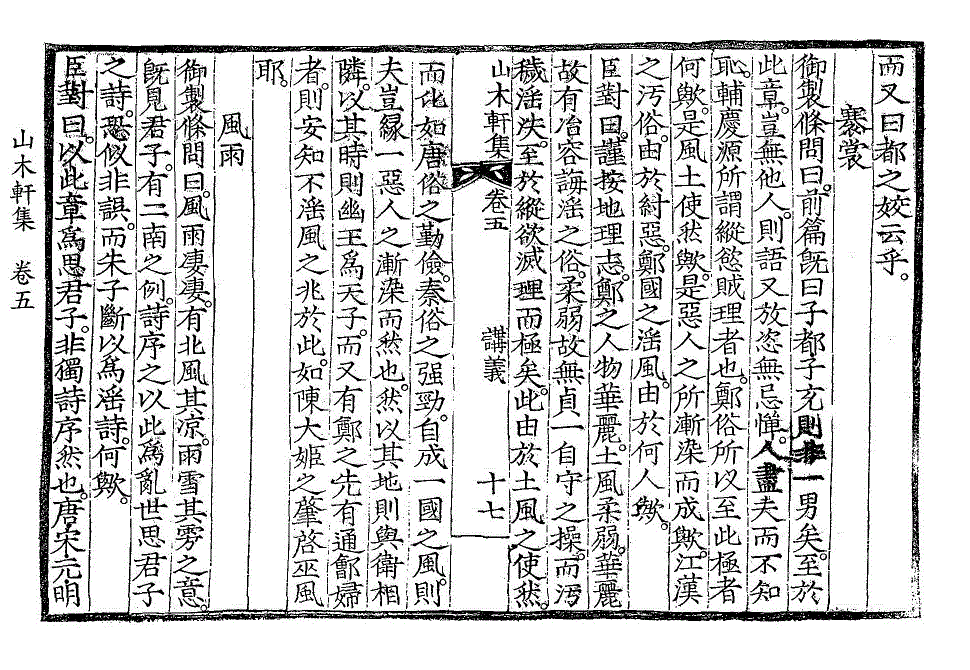 而又曰都之姣云乎。
而又曰都之姣云乎。褰裳
御制条问曰。前篇既曰子都,子充则非一男矣。至于此章。岂无他人。则语又放恣无忌惮。人尽夫而不知耻。辅庆源所谓纵欲贼理者也。郑俗所以至此极者何欤。是风土使然欤。是恶人之所渐染而成欤。江汉之污俗。由于纣恶。郑国之淫风。由于何人欤。
臣对曰。谨按地理志。郑之人物华丽。土风柔弱。华丽故有冶容诲淫之俗。柔弱故无贞一自守之操。而污秽淫泆。至于纵欲灭理而极矣。此由于土风之使然。而比如唐俗之勤俭。秦俗之强劲。自成一国之风。则夫岂缘一恶人之渐染而然也。然以其地则与卫相邻。以其时则幽王为天子。而又有郑之先有通郐妇者。则安知不淫风之兆于此。如陈大姬之肇启巫风耶。
风雨
御制条问曰。风雨凄凄。有北风其凉。雨雪其雱之意。既见君子。有二南之例。诗序之以此为乱世思君子之诗。恐似非误。而朱子断以为淫诗。何欤。
臣对曰。以此章为思君子。非独诗序然也。唐,宋,元,明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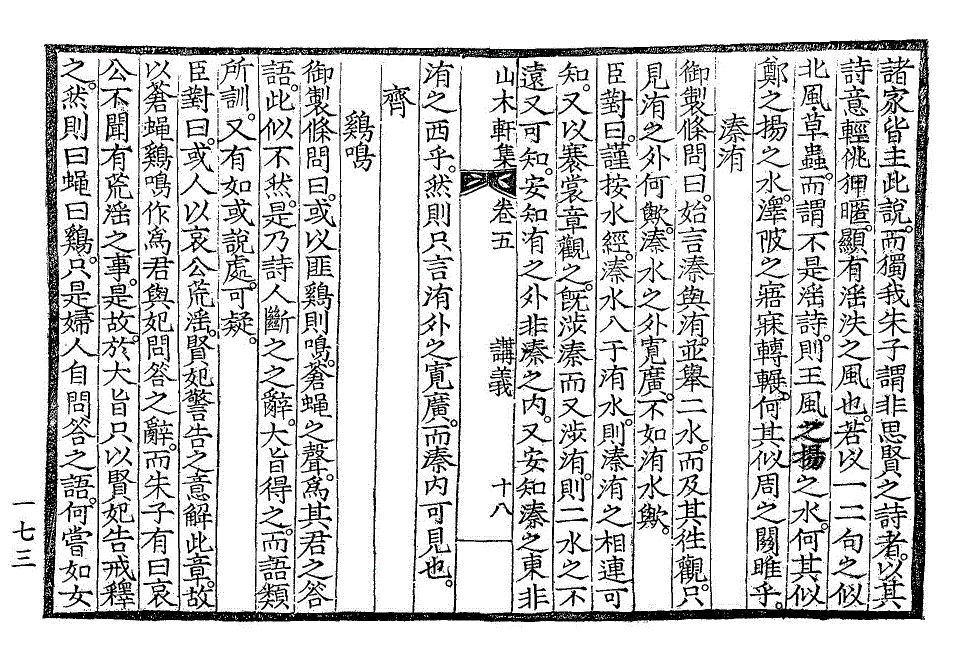 诸家皆主此说。而独我朱子谓非思贤之诗者。以其诗意轻佻狎昵。显有淫泆之风也。若以一二句之似北风,草虫。而谓不是淫诗。则王风之扬之水。何其似郑之扬之水。泽陂之寤寐转辗。何其似周之关雎乎。
诸家皆主此说。而独我朱子谓非思贤之诗者。以其诗意轻佻狎昵。显有淫泆之风也。若以一二句之似北风,草虫。而谓不是淫诗。则王风之扬之水。何其似郑之扬之水。泽陂之寤寐转辗。何其似周之关雎乎。溱洧
御制条问曰。始言溱与洧。并举二水。而及其往观。只见洧之外何欤。溱水之外宽广。不如洧水欤。
臣对曰。谨按水经。溱水入于洧水。则溱洧之相连可知。又以褰裳章观之。既涉溱而又涉洧。则二水之不远又可知。安知有之外非溱之内。又安知溱之东非洧之西乎。然则只言洧外之宽广。而溱内可见也。
齐
鸡鸣
御制条问曰。或以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为其君之答语。此似不然。是乃诗人断之之辞。大旨得之。而语类所训。又有如或说处。可疑。
臣对曰。或人以哀公荒淫。贤妃警告之意解此章。故以苍蝇鸡鸣作为君与妃问答之辞。而朱子有曰哀公不闻有荒淫之事。是故。于大旨只以贤妃告戒释之。然则曰蝇曰鸡。只是妇人自问答之语。何尝如女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4H 页
 曰鸡鸣。士曰昧朝之一例语乎。集传是朱子已勘之正本。则恐当以此为归。
曰鸡鸣。士曰昧朝之一例语乎。集传是朱子已勘之正本。则恐当以此为归。御制条问曰。以蝇声虫飞观之。夏夜也。我东先儒言夏夜苦短。而能自早兴为尤难。然则夏夜苦短。故尤恐其或晚欤。
臣对曰。冬之永夜。固亦不懈警畏之念。而夏夜易曙。尤恐或晚。诚如 圣教。
还
御制条问曰。从两牡兮。是何兽之牡欤。
臣对曰。诗曰奉时辰牡。宗庙之荐。公宫之献。以牡为贵。而古者冬荐狼。夏荐麋。春秋鹿豕则狼麋鹿豕之牡。皆可用矣。此章之从肩。秋也。从狼。冬也。中间一章。兼四时而言。则狼麋鹿豕。皆在一牡字之中矣。
著
御制条问曰。此诗不详为何人之婚姻。而孔氏以著为宁。宁是人君视朝所宁立处。则此为国君之婚姻。千乘之婚而不亲迎。则礼义之坏可知也。然朱子语类。论充耳以为五等之爵所用。青黄莹只是押韵。如卫风良马六之。六马是天子之礼。卫人安得用。观此训。有若借用者然。贵贱之分截严。名物借用。不亦僭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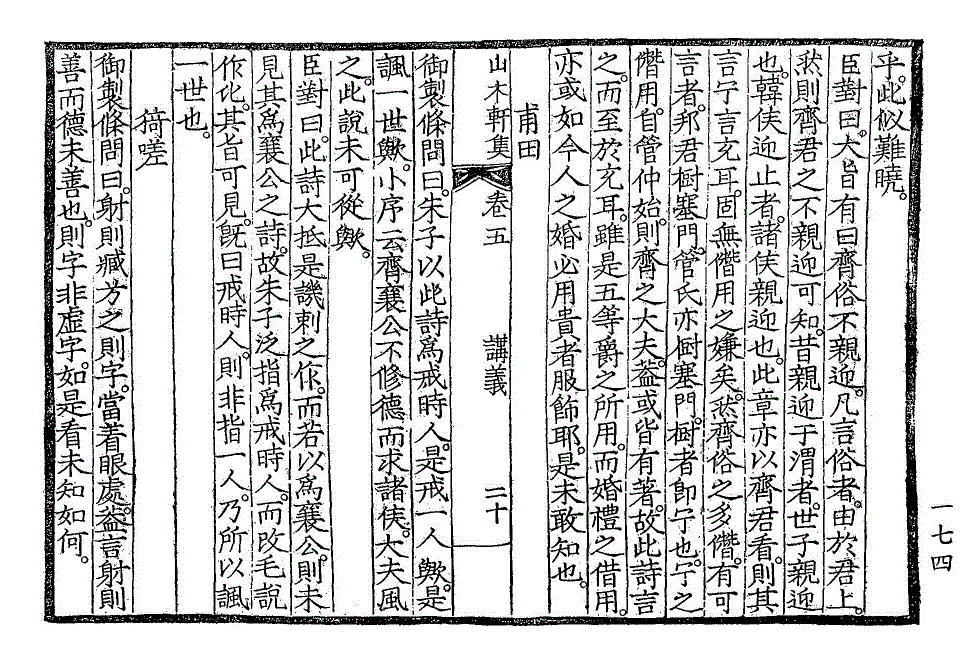 乎。此似难晓。
乎。此似难晓。臣对曰。大旨有曰齐俗不亲迎。凡言俗者。由于君上。然则齐君之不亲迎可知。昔亲迎于渭者。世子亲迎也。韩侯迎止者。诸侯亲迎也。此章亦以齐君看。则其言宁言充耳。固无僭用之嫌矣。然齐俗之多僭。有可言者。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树者即宁也。宁之僭用。自管仲始。则齐之大夫。盖或皆有著。故此诗言之。而至于充耳。虽是五等爵之所用。而婚礼之借用。亦或如今人之婚必用贵者服饰耶。是未敢知也。
甫田
御制条问曰。朱子以此诗为戒时人。是戒一人欤。是讽一世欤。小序云齐襄公不修德而求诸侯。大夫风之。此说未可从欤。
臣对曰。此诗大抵是讥刺之作。而若以为襄公。则未见其为襄公之诗。故朱子泛指为戒时人。而改毛说作比。其旨可见。既曰戒时人。则非指一人。乃所以讽一世也。
猗嗟
御制条问曰。射则臧兮之则字。当着眼处。盖言射则善而德未善也。则字非虚字。如是看未知如何。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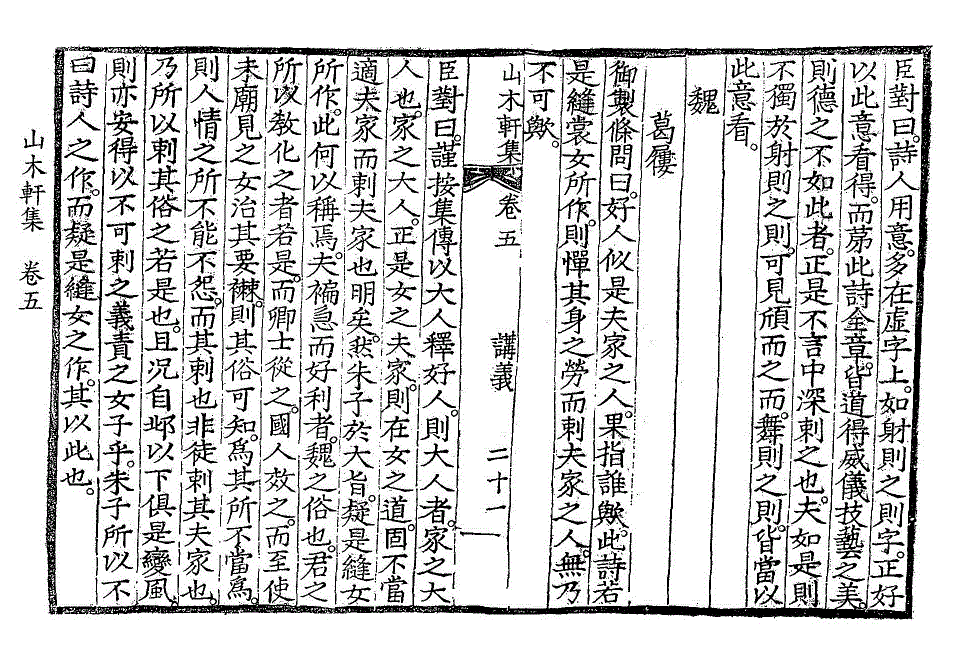 臣对曰。诗人用意。多在虚字上。如射则之则字。正好以此意看得。而第此诗全章。皆道得威仪技艺之美。则德之不如此者。正是不言中深刺之也。夫如是则不独于射则之则。可见颀而之而。舞则之则。皆当以此意看。
臣对曰。诗人用意。多在虚字上。如射则之则字。正好以此意看得。而第此诗全章。皆道得威仪技艺之美。则德之不如此者。正是不言中深刺之也。夫如是则不独于射则之则。可见颀而之而。舞则之则。皆当以此意看。魏
葛屦
御制条问曰。好人似是夫家之人。果指谁欤。此诗若是缝裳女所作。则惮其身之劳而刺夫家之人。无乃不可欤。
臣对曰。谨按集传以大人释好人。则大人者。家之大人也。家之大人。正是女之夫家。则在女之道。固不当适夫家而刺夫家也明矣。然朱子于大旨。疑是缝女所作。此何以称焉。夫褊急而好利者。魏之俗也。君之所以教化之者若是。而卿士从之。国人效之。而至使未庙见之女治其要襋。则其俗可知。为其所不当为。则人情之所不能不怨。而其刺也非徒刺其夫家也。乃所以刺其俗之若是也。且况自邶以下俱是变风。则亦安得以不可刺之义责之女子乎。朱子所以不曰诗人之作。而疑是缝女之作。其以此也。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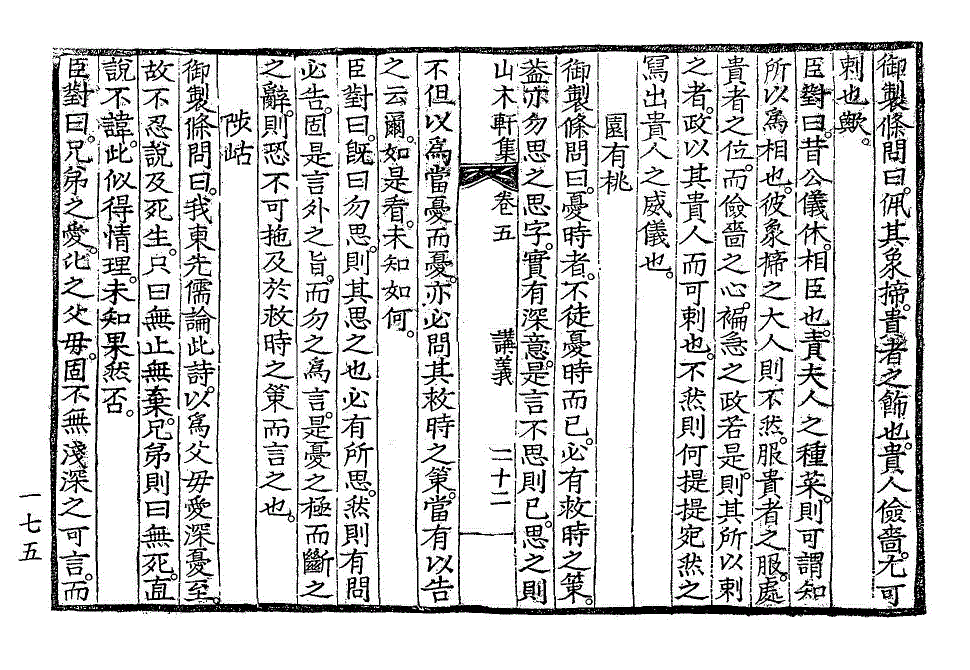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佩其象揥。贵者之饰也。贵人俭啬。尤可刺也欤。
御制条问曰。佩其象揥。贵者之饰也。贵人俭啬。尤可刺也欤。臣对曰。昔公仪休。相臣也。责夫人之种菜。则可谓知所以为相也。彼象揥之大人则不然。服贵者之服。处贵者之位。而俭啬之心。褊急之政若是。则其所以刺之者。政以其贵人而可刺也。不然则何提提宛然之写出贵人之威仪也。
园有桃
御制条问曰。忧时者。不徒忧时而已。必有救时之策。盖亦勿思之思字。实有深意。是言不思则已。思之则不但以为当忧而忧。亦必问其救时之策。当有以告之云尔。如是看。未知如何。
臣对曰。既曰勿思。则其思之也必有所思。然则有问必告。固是言外之旨。而勿之为言。是忧之极而断之之辞。则恐不可拖及于救时之策而言之也。
陟岵
御制条问曰。我东先儒论此诗。以为父母爱深忧至。故不忍说及死生。只曰无止无弃。兄弟则曰无死。直说不讳。此似得情理。未知果然否。
臣对曰。兄弟之爱。比之父母。固不无浅深之可言。而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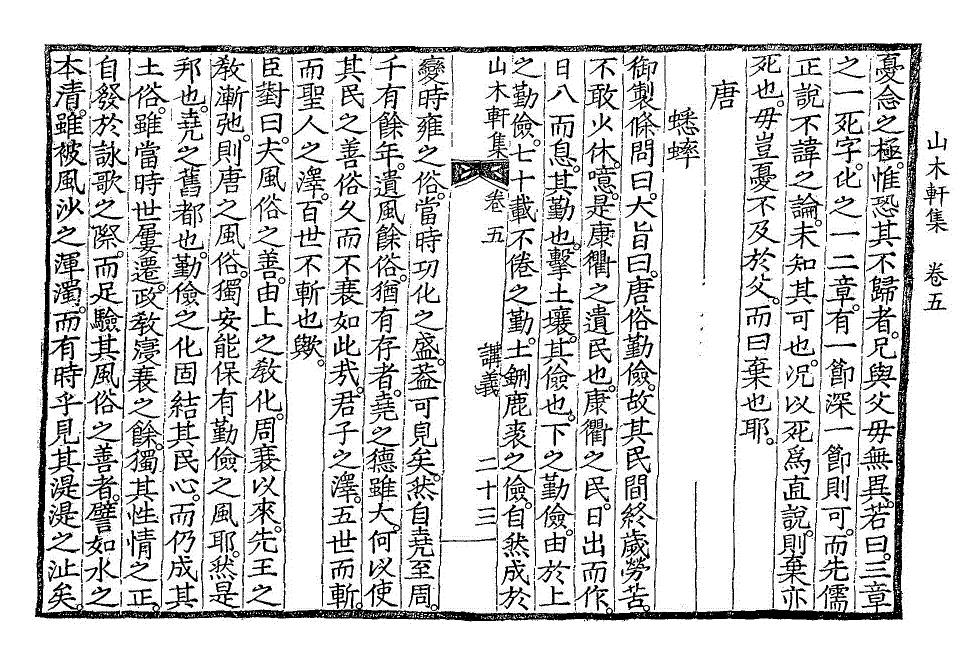 忧念之极。惟恐其不归者。兄与父母无异。若曰。三章之一死字。比之一二章。有一节深一节则可。而先儒正说不讳之论。未知其可也。况以死为直说。则弃亦死也。母岂忧不及于父。而曰弃也耶。
忧念之极。惟恐其不归者。兄与父母无异。若曰。三章之一死字。比之一二章。有一节深一节则可。而先儒正说不讳之论。未知其可也。况以死为直说。则弃亦死也。母岂忧不及于父。而曰弃也耶。唐
蟋蟀
御制条问曰。大旨曰。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噫。是康衢之遗民也。康衢之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勤也。击土壤。其俭也。下之勤俭。由于上之勤俭。七十载不倦之勤。土铏鹿裘之俭。自然成于变时雍之俗。当时功化之盛。盖可见矣。然自尧至周。千有馀年。遗风馀俗。犹有存者。尧之德虽大。何以使其民之善俗久而不衰如此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圣人之泽。百世不斩也欤。
臣对曰。夫风俗之善。由上之教化。周衰以来。先王之教渐弛。则唐之风俗。独安能保有勤俭之风耶。然是邦也。尧之旧都也。勤俭之化固结其民心。而仍成其土俗。虽当时世屡迁。政教寖衰之馀。独其性情之正。自发于咏歌之际。而足验其风俗之善者。譬如水之本清。虽被风沙之浑浊。而有时乎见其湜湜之沚矣。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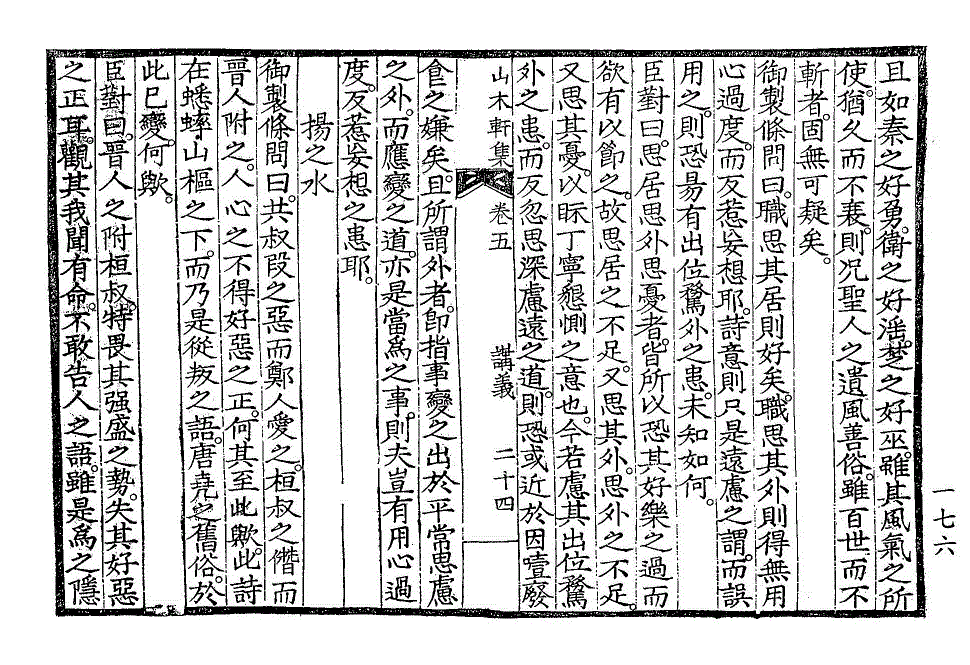 且如秦之好勇。卫之好淫。楚之好巫。虽其风气之所使。犹久而不衰。则况圣人之遗风善俗。虽百世而不斩者。固无可疑矣。
且如秦之好勇。卫之好淫。楚之好巫。虽其风气之所使。犹久而不衰。则况圣人之遗风善俗。虽百世而不斩者。固无可疑矣。御制条问曰。职思其居则好矣。职思其外则得无用心过度。而反惹妄想耶。诗意则只是远虑之谓。而误用之。则恐易有出位骛外之患。未知如何。
臣对曰。思居思外思忧者。皆所以恐其好乐之过而欲有以节之。故思居之不足。又思其外。思外之不足。又思其忧。以视丁宁恳恻之意也。今若虑其出位骛外之患。而反忽思深虑远之道。则恐或近于因噎废食之嫌矣。且所谓外者。即指事变之出于平常思虑之外。而应变之道。亦是当为之事。则夫岂有用心过度。反惹妄想之患耶。
扬之水
御制条问曰。共叔段之恶而郑人爱之。桓叔之僭而晋人附之。人心之不得好恶之正。何其至此欤。此诗在蟋蟀,山枢之下。而乃是从叛之语。唐尧之旧俗。于此已变。何欤。
臣对曰。晋人之附桓叔。特畏其强盛之势。失其好恶之正耳。观其我闻有命。不敢告人之语。虽是为之隐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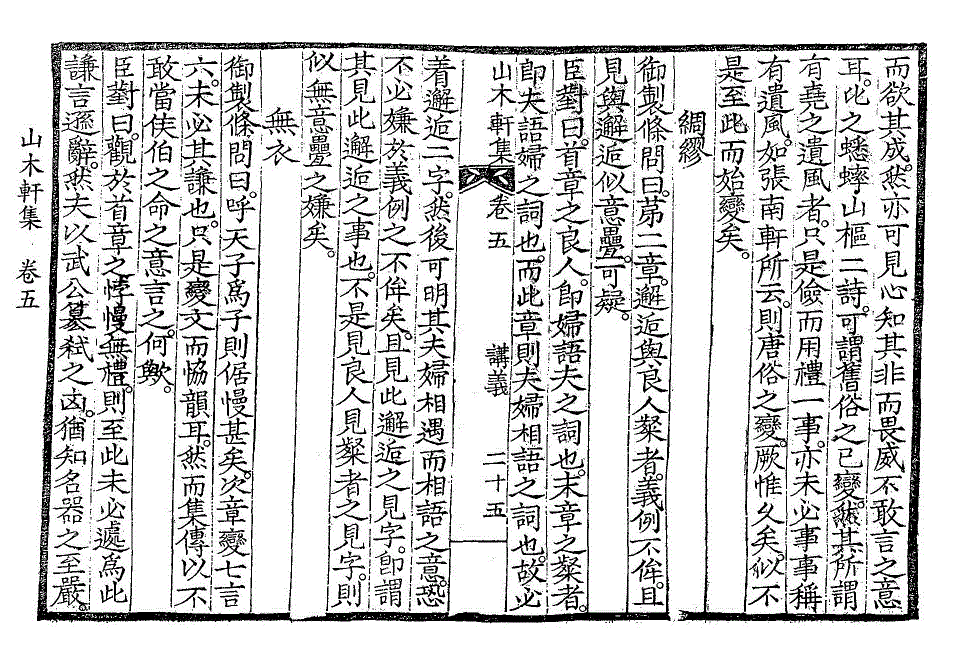 而欲其成。然亦可见心知其非而畏威不敢言之意耳。比之蟋蟀,山枢二诗。可谓旧俗之已变。然其所谓有尧之遗风者。只是俭而用礼一事。亦未必事事称有遗风。如张南轩所云。则唐俗之变。厥惟久矣。似不是至此而始变矣。
而欲其成。然亦可见心知其非而畏威不敢言之意耳。比之蟋蟀,山枢二诗。可谓旧俗之已变。然其所谓有尧之遗风者。只是俭而用礼一事。亦未必事事称有遗风。如张南轩所云。则唐俗之变。厥惟久矣。似不是至此而始变矣。绸缪
御制条问曰。第二章。邂逅与良人粲者。义例不侔。且见与邂逅似意叠。可疑。
臣对曰。首章之良人。即妇语夫之词也。末章之粲者。即夫语妇之词也。而此章则夫妇相语之词也。故必着邂逅二字。然后可明其夫妇相遇而相语之意。恐不必嫌于义例之不侔矣。且见此邂逅之见字。即谓其见此邂逅之事也。不是见良人见粲者之见字。则似无意叠之嫌矣。
无衣
御制条问曰。呼天子为子则倨慢甚矣。次章变七言六。未必其谦也。只是变文而协韵耳。然而集传以不敢当侯伯之命之意言之。何欤。
臣对曰。观于首章之悖慢无礼。则至此未必遽为此谦言逊辞。然夫以武公篡弑之凶。犹知名器之至严。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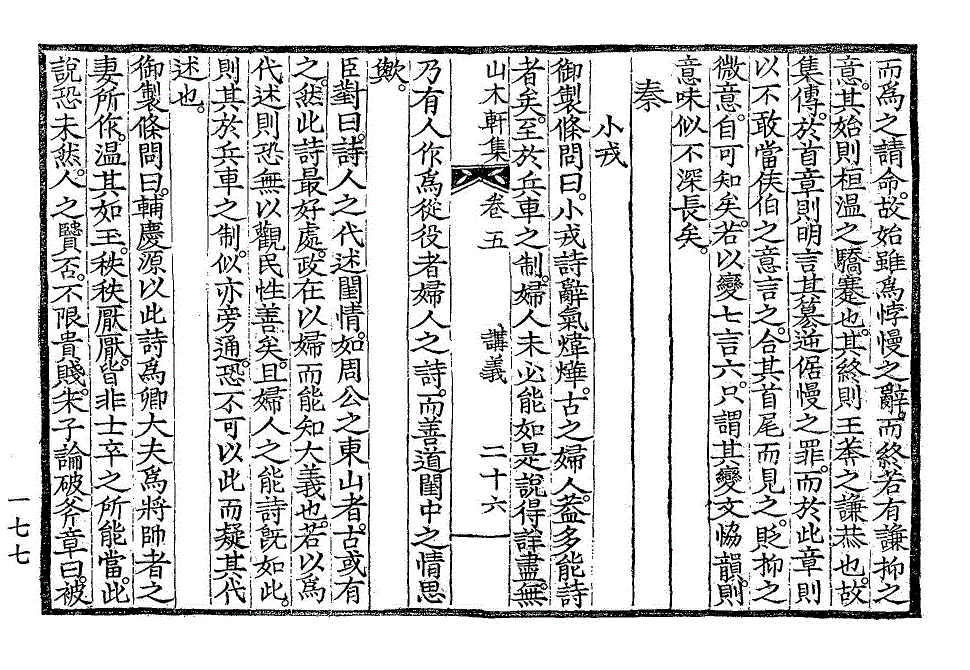 而为之请命。故始虽为悖慢之辞。而终若有谦抑之意。其始则桓温之骄蹇也。其终则王莽之谦恭也。故集传。于首章则明言其篡逆倨慢之罪。而于此章则以不敢当侯伯之意言之。合其首尾而见之。贬抑之微意。自可知矣。若以变七言六。只谓其变文协韵。则意味似不深长矣。
而为之请命。故始虽为悖慢之辞。而终若有谦抑之意。其始则桓温之骄蹇也。其终则王莽之谦恭也。故集传。于首章则明言其篡逆倨慢之罪。而于此章则以不敢当侯伯之意言之。合其首尾而见之。贬抑之微意。自可知矣。若以变七言六。只谓其变文协韵。则意味似不深长矣。秦
小戎
御制条问曰。小戎诗辞气炜烨。古之妇人。盖多能诗者矣。至于兵车之制。妇人未必能如是说得详尽。无乃有人作为从役者妇人之诗。而善道闺中之情思欤。
臣对曰。诗人之代述闺情。如周公之东山者。古或有之。然此诗最好处。政在以妇而能知大义也。若以为代述则恐无以观民性善矣。且妇人之能诗既如此。则其于兵车之制。似亦旁通。恐不可以此而疑其代述也。
御制条问曰。辅庆源以此诗为卿大夫为将帅者之妻所作。温其如玉。秩秩厌厌。皆非士卒之所能当。此说恐未然。人之贤否。不限贵贱。朱子论破斧章曰。被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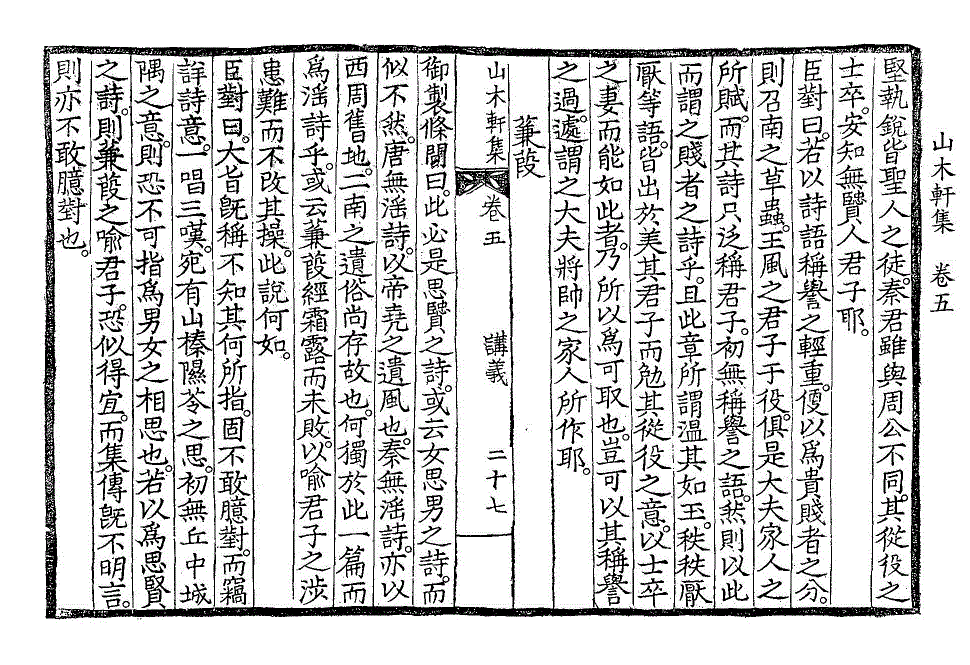 坚执锐皆圣人之徒。秦君虽与周公不同。其从役之士卒。安知无贤人君子耶。
坚执锐皆圣人之徒。秦君虽与周公不同。其从役之士卒。安知无贤人君子耶。臣对曰。若以诗语称誉之轻重。便以为贵贱者之分。则召南之草虫。王风之君子于役。俱是大夫家人之所赋。而其诗只泛称君子。初无称誉之语。然则以此而谓之贱者之诗乎。且此章所谓温其如玉。秩秩厌厌等语。皆出于美其君子而勉其从役之意。以士卒之妻而能如此者。乃所以为可取也。岂可以其称誉之过。遽谓之大夫将帅之家人所作耶。
蒹葭
御制条问曰。此必是思贤之诗。或云女思男之诗。而似不然。唐无淫诗。以帝尧之遗风也。秦无淫诗。亦以西周旧地。二南之遗俗尚存故也。何独于此一篇而为淫诗乎。或云蒹葭经霜露而未败。以喻君子之涉患难而不改其操。此说何如。
臣对曰。大旨既称不知其何所指。固不敢臆对。而窃详诗意。一唱三叹。宛有山榛隰苓之思。初无丘中城隅之意。则恐不可指为男女之相思也。若以为思贤之诗。则蒹葭之喻君子。恐似得宜。而集传既不明言。则亦不敢臆对也。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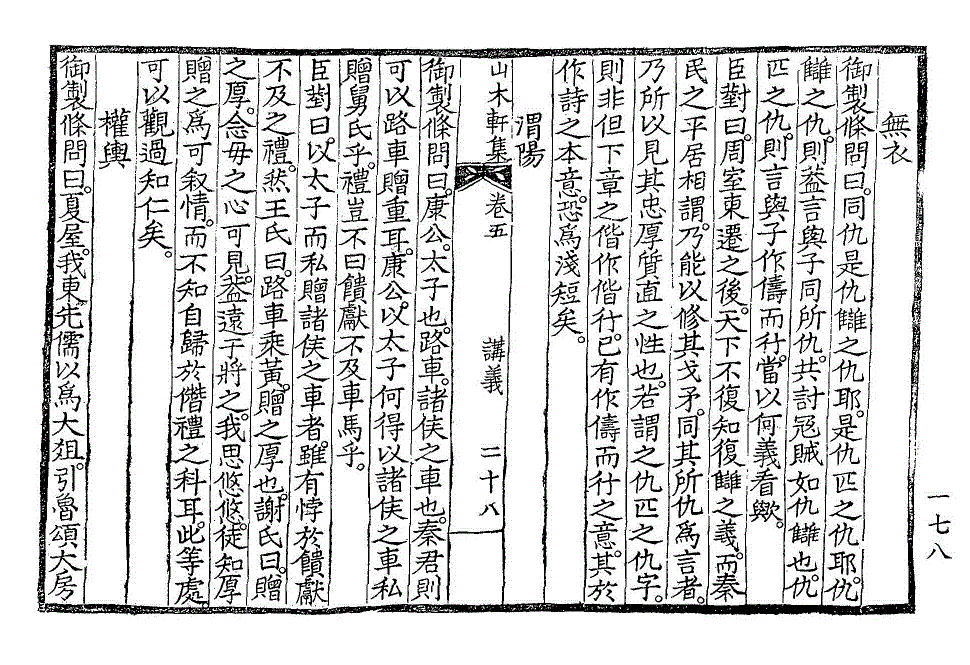 无衣
无衣御制条问曰。同仇是仇雠之仇耶。是仇匹之仇耶。仇雠之仇。则盖言与子同所仇。共讨寇贼如仇雠也。仇匹之仇。则言与子作俦而行。当以何义看欤。
臣对曰。周室东迁之后。天下不复知复雠之义。而秦民之平居相谓。乃能以修其戈矛。同其所仇为言者。乃所以见其忠厚质直之性也。若谓之仇匹之仇字。则非但下章之偕作偕行。已有作俦而行之意。其于作诗之本意。恐为浅短矣。
渭阳
御制条问曰。康公。太子也。路车。诸侯之车也。秦君则可以路车赠重耳。康公。以太子何得以诸侯之车私赠舅氏乎。礼岂不曰馈献不及车马乎。
臣对曰。以太子而私赠诸侯之车者。虽有悖于馈献不及之礼。然王氏曰。路车乘黄。赠之厚也。谢氏曰。赠之厚。念母之心可见。盖远于将之。我思悠悠。徒知厚赠之为可叙情。而不知自归于僭礼之科耳。此等处。可以观过知仁矣。
权舆
御制条问曰。夏屋。我东先儒以为大俎。引鲁颂大房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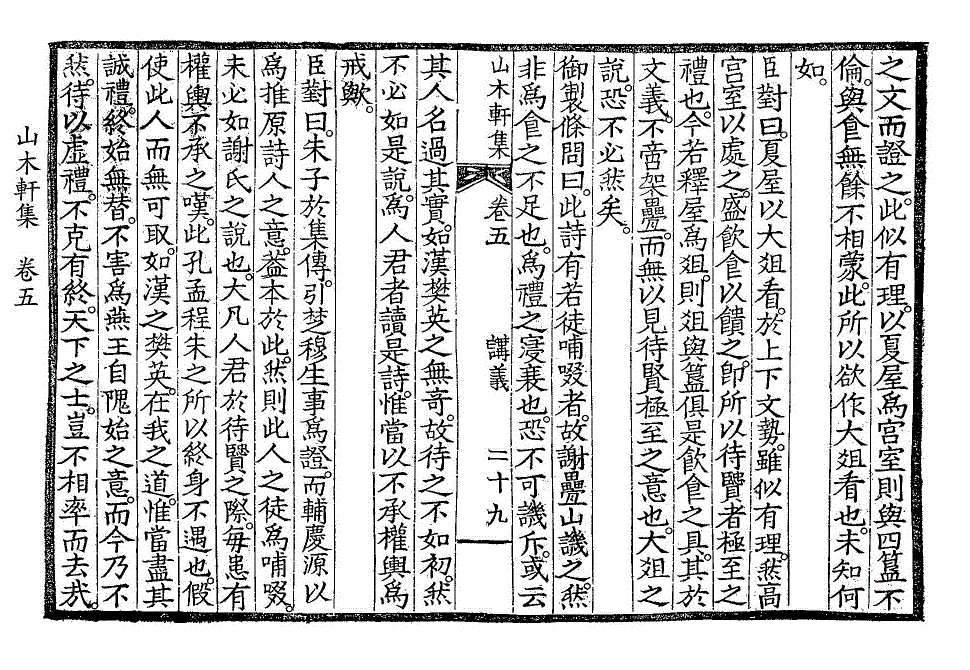 之文而證之。此似有理。以夏屋为宫室则与四簋不伦。与食无馀不相蒙。此所以欲作大俎看也。未知何如。
之文而證之。此似有理。以夏屋为宫室则与四簋不伦。与食无馀不相蒙。此所以欲作大俎看也。未知何如。臣对曰。夏屋以大俎看。于上下文势。虽似有理。然高宫室以处之。盛饮食以馈之。即所以待贤者极至之礼也。今若释屋为俎。则俎与簋俱是饮食之具。其于文义。不啻架叠。而无以见待贤极至之意也。大俎之说。恐不必然矣。
御制条问曰。此诗有若徒哺啜者。故谢叠山讥之。然非为食之不足也。为礼之寖衰也。恐不可讥斥。或云其人名过其实。如汉樊英之无奇。故待之不如初。然不必如是说。为人君者读是诗。惟当以不承权舆为戒欤。
臣对曰。朱子于集传。引楚穆生事为證。而辅庆源以为推原诗人之意。盖本于此。然则此人之徒为哺啜。未必如谢氏之说也。大凡人君于待贤之际。每患有权舆不承之叹。此孔孟程朱之所以终身不遇也。假使此人而无可取。如汉之樊英。在我之道。惟当尽其诚礼。终始无替。不害为燕王自隗始之意。而今乃不然。待以虚礼。不克有终。天下之士。岂不相率而去哉。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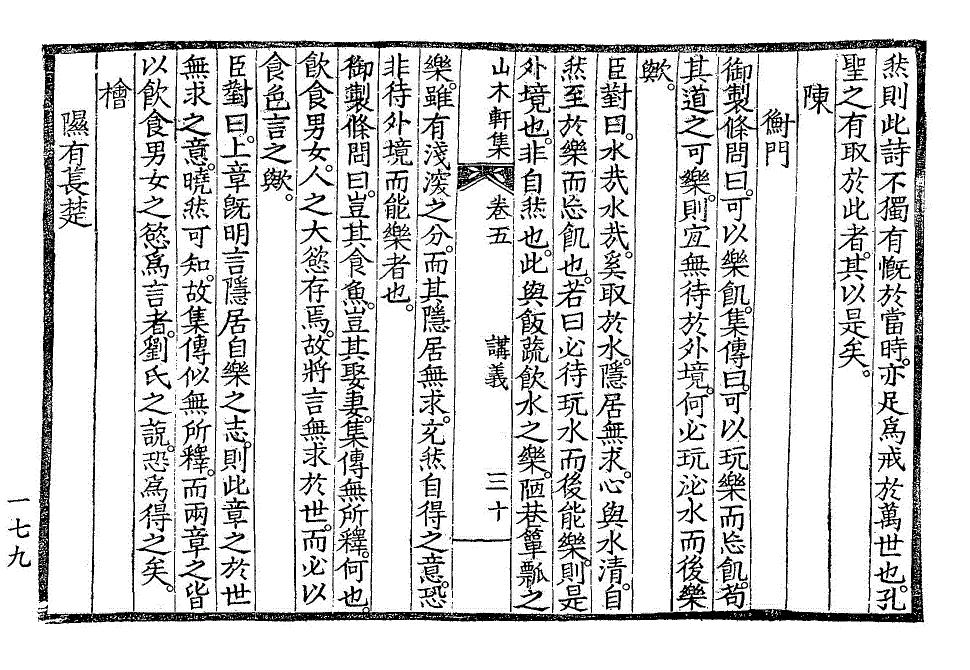 然则此诗不独有慨于当时。亦足为戒于万世也。孔圣之有取于此者。其以是矣。
然则此诗不独有慨于当时。亦足为戒于万世也。孔圣之有取于此者。其以是矣。陈
衡门
御制条问曰。可以乐饥。集传曰。可以玩乐而忘饥。苟其道之可乐。则宜无待于外境。何必玩泌水而后乐欤。
臣对曰。水哉水哉。奚取于水。隐居无求。心与水清。自然至于乐而忘饥也。若曰必待玩水而后能乐。则是外境也。非自然也。此与饭蔬饮水之乐。陋巷箪瓢之乐。虽有浅深之分。而其隐居无求。充然自得之意。恐非待外境而能乐者也。
御制条问曰。岂其食鱼。岂其娶妻。集传无所释。何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将言无求于世。而必以食色言之欤。
臣对曰。上章既明言隐居自乐之志。则此章之于世无求之意。晓然可知。故集传似无所释。而两章之皆以饮食男女之欲为言者。刘氏之说。恐为得之矣。
桧
隰有苌楚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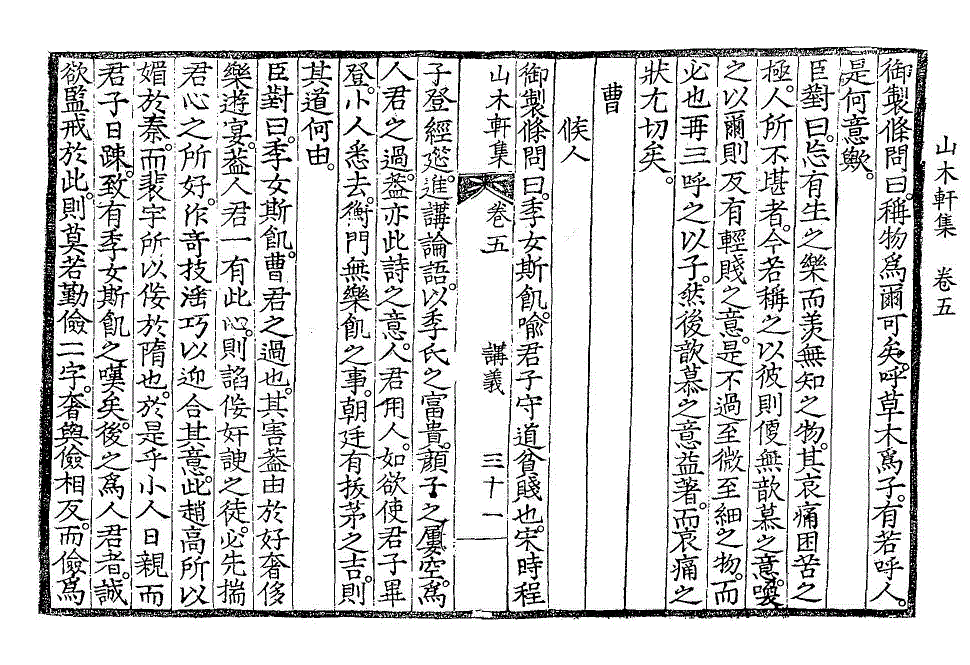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称物为尔可矣。呼草木为子。有若呼人。是何意欤。
御制条问曰。称物为尔可矣。呼草木为子。有若呼人。是何意欤。臣对曰。忘有生之乐而羡无知之物。其哀痛困苦之极。人所不堪者。今若称之以彼则便无歆慕之意。唤之以尔则反有轻贱之意。是不过至微至细之物。而必也再三呼之以子。然后歆慕之意益著。而哀痛之状尤切矣。
曹
候人
御制条问曰。季女斯饥。喻君子守道贫贱也。宋时程子登经筵。进讲论语。以季氏之富贵。颜子之屡空。为人君之过。盖亦此诗之意。人君用人。如欲使君子毕登。小人悉去。衡门无乐饥之事。朝廷有拔茅之吉。则其道何由。
臣对曰。季女斯饥。曹君之过也。其害盖由于好奢侈乐游宴。盖人君一有此心。则谄佞奸谀之徒。必先揣君心之所好。作奇技淫巧以迎合其意。此赵高所以媚于秦。而裴宇所以佞于隋也。于是乎小人日亲而君子日疏。致有季女斯饥之叹矣。后之为人君者。诚欲监戒于此。则莫若勤俭二字。奢与俭相反。而俭为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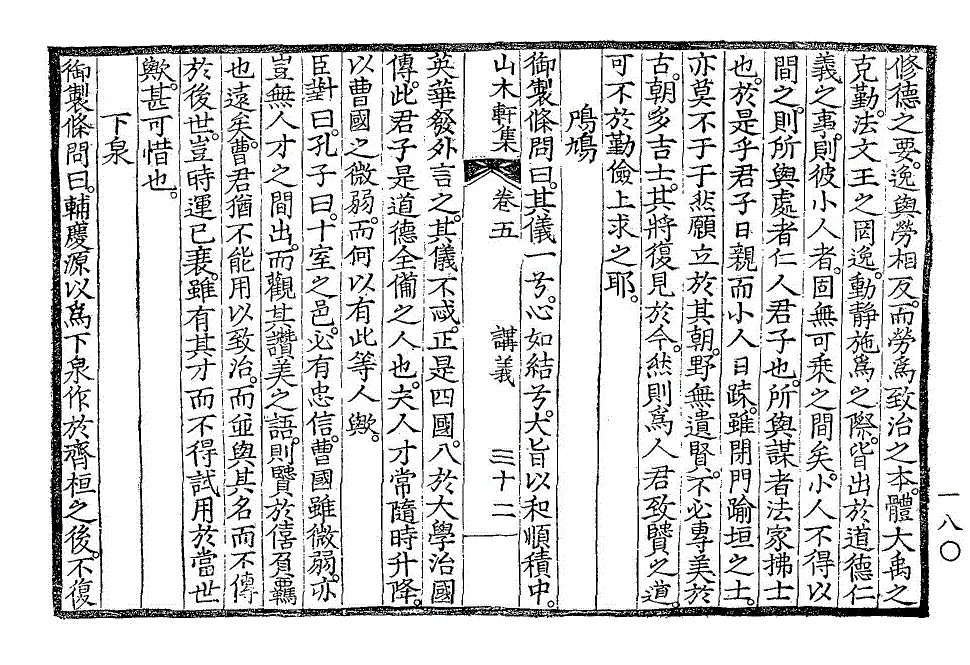 修德之要。逸与劳相反。而劳为致治之本。体大禹之克勤。法文王之罔逸。动静施为之际。皆出于道德仁义之事。则彼小人者。固无可乘之间矣。小人不得以间之。则所与处者仁人君子也。所与谋者法家拂士也。于是乎君子日亲而小人日疏。虽闭门踰垣之士。亦莫不于于然愿立于其朝。野无遗贤。不必专美于古。朝多吉士。其将复见于今。然则为人君致贤之道。可不于勤俭上求之耶。
修德之要。逸与劳相反。而劳为致治之本。体大禹之克勤。法文王之罔逸。动静施为之际。皆出于道德仁义之事。则彼小人者。固无可乘之间矣。小人不得以间之。则所与处者仁人君子也。所与谋者法家拂士也。于是乎君子日亲而小人日疏。虽闭门踰垣之士。亦莫不于于然愿立于其朝。野无遗贤。不必专美于古。朝多吉士。其将复见于今。然则为人君致贤之道。可不于勤俭上求之耶。鸤鸠
御制条问曰。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大旨以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言之。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入于大学治国传。此君子是道德全备之人也。夫人才常随时升降。以曹国之微弱。而何以有此等人欤。
臣对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曹国虽微弱。亦岂无人才之间出。而观其赞美之语。则贤于僖负羁也远矣。曹君犹不能用以致治。而并与其名而不传于后世。岂时运已衰。虽有其才而不得试用于当世欤。甚可惜也。
下泉
御制条问曰。辅庆源以为下泉作于齐桓之后。不复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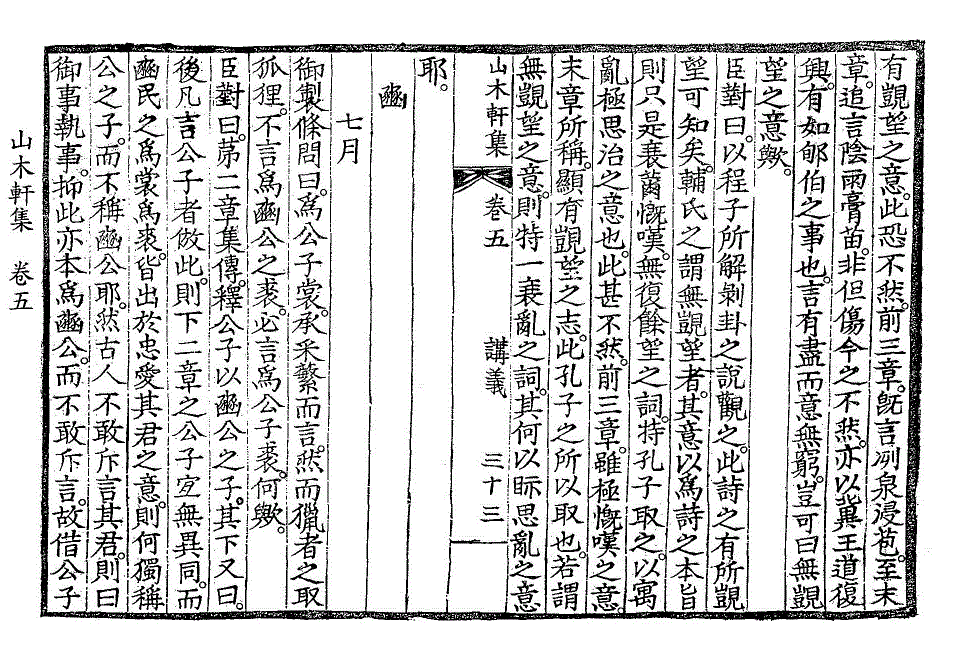 有觊望之意。此恐不然。前三章。既言冽泉浸苞。至末章。追言阴雨膏苗。非但伤今之不然。亦以冀王道复兴。有如郇伯之事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岂可曰无觊望之意欤。
有觊望之意。此恐不然。前三章。既言冽泉浸苞。至末章。追言阴雨膏苗。非但伤今之不然。亦以冀王道复兴。有如郇伯之事也。言有尽而意无穷。岂可曰无觊望之意欤。臣对曰。以程子所解剥卦之说观之。此诗之有所觊望可知矣。辅氏之谓无觊望者。其意以为诗之本旨则只是衰薾慨叹。无复馀望之词。持孔子取之。以寓乱极思治之意也。此甚不然。前三章。虽极慨叹之意。末章所称。显有觊望之志。此孔子之所以取也。若谓无觊望之意。则特一衰乱之词。其何以视思乱之意耶。
豳
七月
御制条问曰。为公子裳。承采蘩而言。然而猎者之取狐狸。不言为豳公之裘。必言为公子裘。何欤。
臣对曰。第二章集传。释公子以豳公之子。其下又曰。后凡言公子者仿此。则下二章之公子宜无异同。而豳民之为裳为裘。皆出于忠爱其君之意。则何独称公之子。而不称豳公耶。然古人不敢斥言其君。则曰御事执事。抑此亦本为豳公。而不敢斥言。故借公子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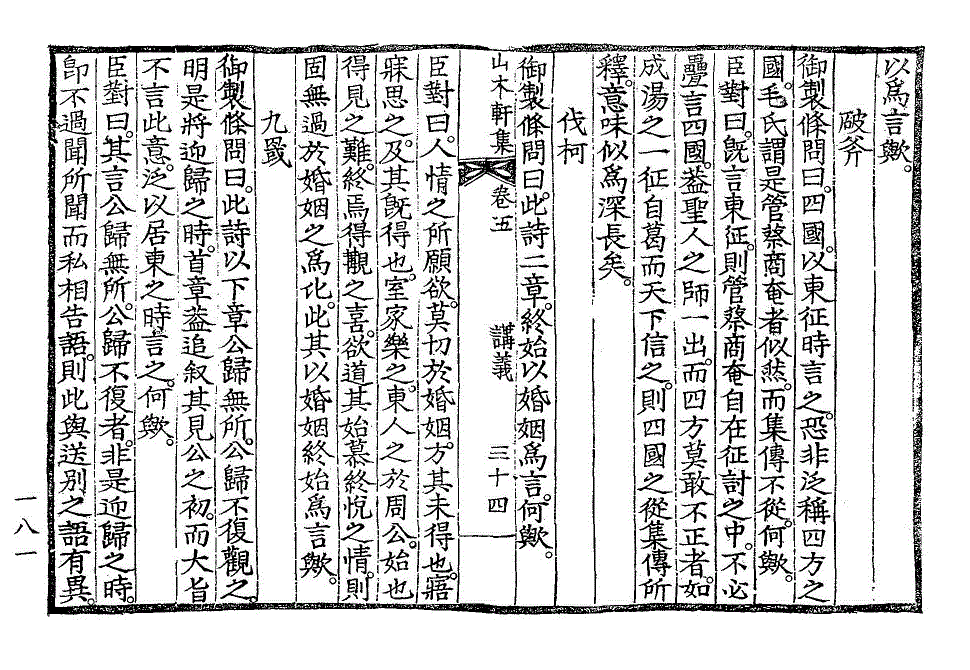 以为言欤。
以为言欤。破斧
御制条问曰。四国。以东征时言之。恐非泛称四方之国。毛氏谓是管蔡商奄者似然。而集传不从。何欤。
臣对曰。既言东征。则管蔡商奄自在征讨之中。不必叠言四国。盖圣人之师一出。而四方莫敢不正者。如成汤之一征自葛而天下信之。则四国之从集传所释。意味似为深长矣。
伐柯
御制条问曰。此诗二章。终始以婚姻为言。何欤。
臣对曰。人情之所愿欲。莫切于婚姻。方其未得也。寤寐思之。及其既得也。室家乐之。东人之于周公。始也得见之难。终焉得觏之喜。欲道其始慕终悦之情。则固无过于婚姻之为比。此其以婚姻终始为言欤。
九罭
御制条问曰。此诗以下章公归无所。公归不复观之。明是将迎归之时。首章盖追叙其见公之初。而大旨不言此意。泛以居东之时言之。何欤。
臣对曰。其言公归无所。公归不复者。非是迎归之时。即不过闻所闻而私相告语。则此与送别之语有异。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2H 页
 首章所谓我觏之子者。恐非追叙之意。则大旨之泛以居东时为言者。其以是欤。
首章所谓我觏之子者。恐非追叙之意。则大旨之泛以居东时为言者。其以是欤。御制条问曰。无以之以字。当着眼看。明是东人请留之词。然非敢直请于王。私相言之如此欤。
臣对曰。此则明是东人请留之词。而集传所记。史籍所载。元无东人请王留公之事。则其为私相言之者无疑矣。
狼跋
御制条问曰。此亦似东人之诗。而大旨泛称诗人。何欤。
臣对曰。伐柯,九罭二篇。皆叙其一方喜悦之情。则大旨固当以为东人之作。而至于此章则虽亦似居东之诗。然圣人之善处患难。让美自晦。其威仪之安閒。德音之隆盛。天下人之所共瞻仰而爱慕者。则固非一方之所可私议者。此集传所以不称东人之诗。而归之诗人之赞美者欤。
御制条问曰。圣人之处患难不失其常。不独于步履间见之。而必称赤舄几几。何欤。岂九容之中。足容重为最难也欤。
臣对曰。自周公而言之。则虽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
山木轩集卷之五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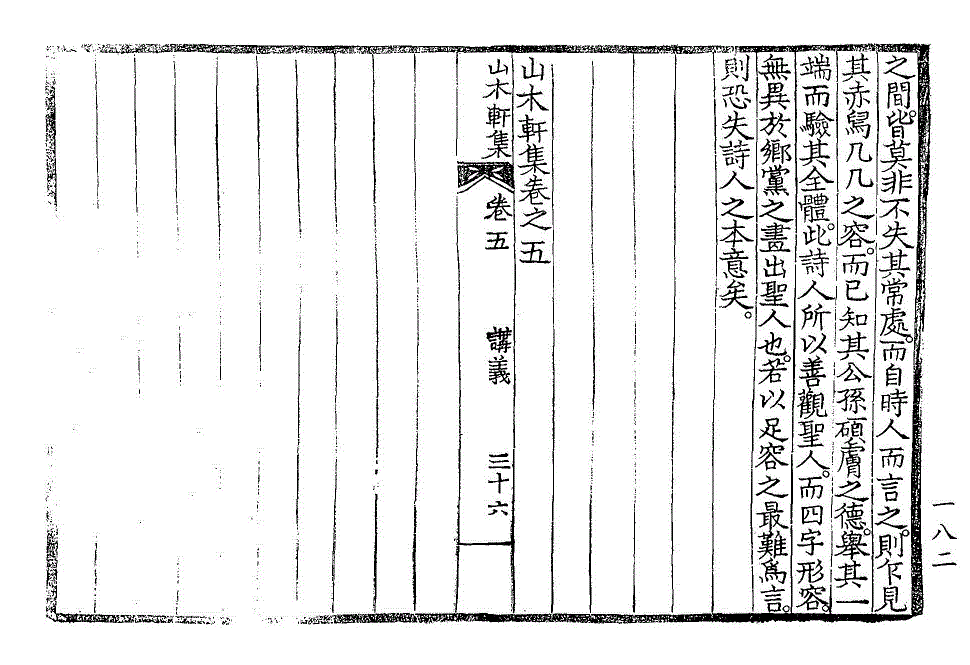 之间。皆莫非不失其常处。而自时人而言之。则乍见其赤舄几几之容。而已知其公孙硕肤之德。举其一端而验其全体。此诗人所以善观圣人。而四字形容。无异于乡党之画出圣人也。若以足容之最难为言。则恐失诗人之本意矣。
之间。皆莫非不失其常处。而自时人而言之。则乍见其赤舄几几之容。而已知其公孙硕肤之德。举其一端而验其全体。此诗人所以善观圣人。而四字形容。无异于乡党之画出圣人也。若以足容之最难为言。则恐失诗人之本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