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x 页
山木轩集卷之四
讲义
讲义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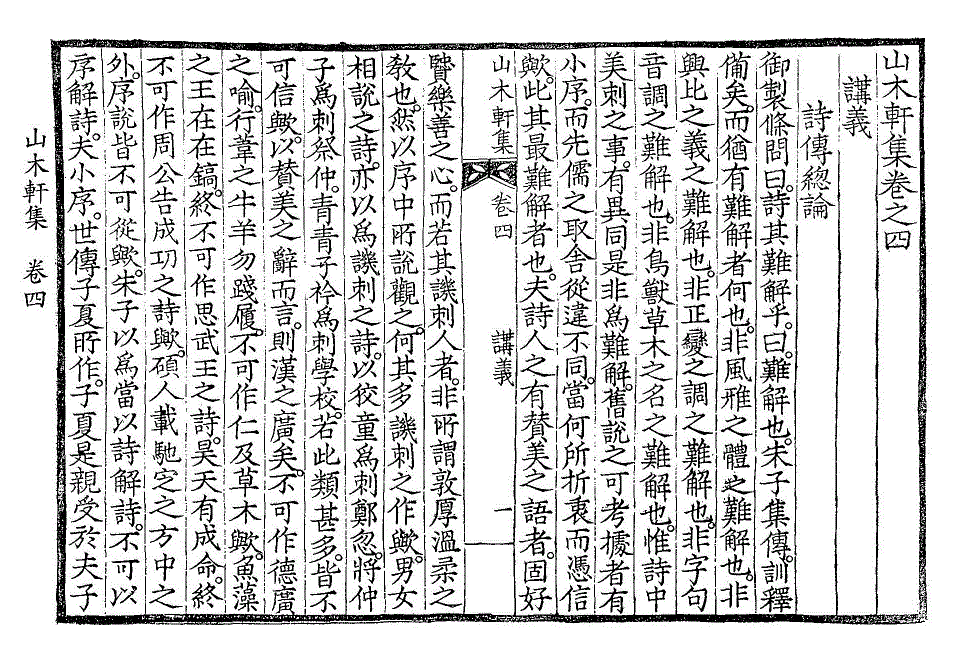 诗传总论
诗传总论御制条问曰。诗其难解乎。曰。难解也。朱子集传。训释备矣。而犹有难解者何也。非风雅之体之难解也。非兴比之义之难解也。非正变之调之难解也。非字句音调之难解也。非鸟兽草木之名之难解也。惟诗中美刺之事。有异同是非为难解。旧说之可考据者有小序。而先儒之取舍从违不同。当何所折衷而凭信欤。此其最难解者也。夫诗人之有赞美之语者。固好贤乐善之心。而若其讥刺人者。非所谓敦厚温柔之教也。然以序中所说观之。何其多讥刺之作欤。男女相说之诗。亦以为讥刺之诗。以狡童为刺郑忽。将仲子为刺祭仲。青青子衿为刺学校。若此类甚多。皆不可信欤。以赞美之辞而言。则汉之广矣。不可作德广之喻。行苇之牛羊勿践履。不可作仁及草木欤。鱼藻之王在在镐。终不可作思武王之诗。昊天有成命。终不可作周公告成功之诗欤。硕人载驰定之方中之外。序说皆不可从欤。朱子以为当以诗解诗。不可以序解诗。夫小序。世传子夏所作。子夏是亲受于夫子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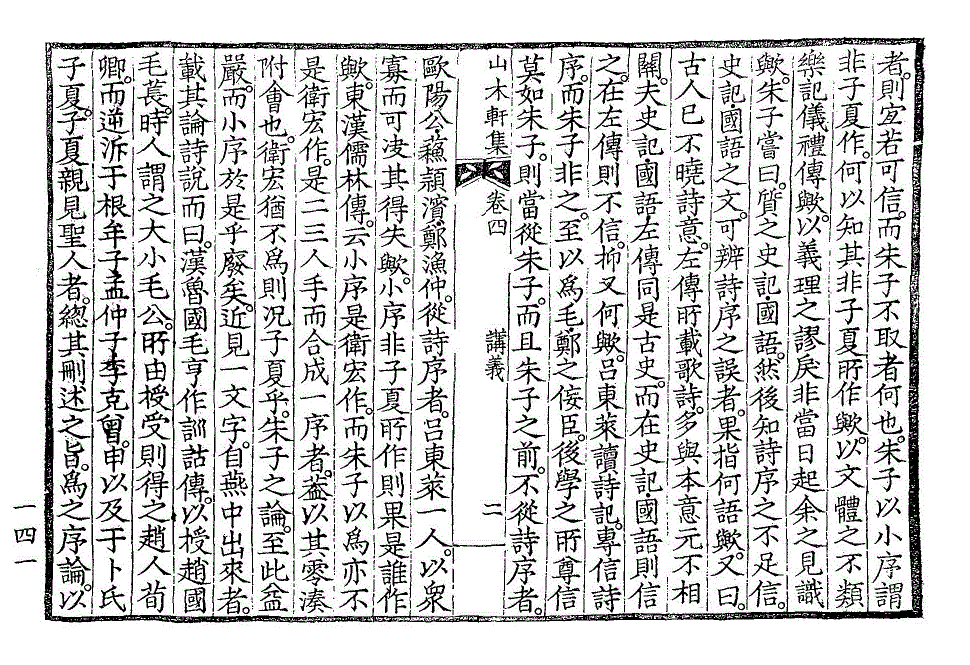 者。则宜若可信。而朱子不取者何也。朱子以小序谓非子夏作。何以知其非子夏所作欤。以文体之不类乐记仪礼传欤。以义理之谬戾非当日起余之见识欤。朱子尝曰。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不足信。史记,国语之文。可辨诗序之误者。果指何语欤。又曰。古人已不晓诗意。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夫史记,国语,左传同是古史。而在史记,国语则信之。在左传则不信。抑又何欤。吕东莱读诗记。专信诗序。而朱子非之。至以为毛,郑之佞臣。后学之所尊信莫如朱子。则当从朱子。而且朱子之前。不从诗序者。欧阳公,苏颖滨,郑渔仲。从诗序者。吕东莱一人。以众寡而可决其得失欤。小序非子夏所作则果是谁作欤。东汉儒林传。云小序是卫宏作。而朱子以为亦不是卫宏作。是二三人手而合成一序者。盖以其零凑附会也。卫宏犹不为则况子夏乎。朱子之论。至此益严。而小序于是乎废矣。近见一文字。自燕中出来者。载其论诗说而曰。汉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之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则得之赵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于卜氏子夏。子夏亲见圣人者。总其删述之旨。为之序论。以
者。则宜若可信。而朱子不取者何也。朱子以小序谓非子夏作。何以知其非子夏所作欤。以文体之不类乐记仪礼传欤。以义理之谬戾非当日起余之见识欤。朱子尝曰。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不足信。史记,国语之文。可辨诗序之误者。果指何语欤。又曰。古人已不晓诗意。左传所载歌诗。多与本意元不相关。夫史记,国语,左传同是古史。而在史记,国语则信之。在左传则不信。抑又何欤。吕东莱读诗记。专信诗序。而朱子非之。至以为毛,郑之佞臣。后学之所尊信莫如朱子。则当从朱子。而且朱子之前。不从诗序者。欧阳公,苏颖滨,郑渔仲。从诗序者。吕东莱一人。以众寡而可决其得失欤。小序非子夏所作则果是谁作欤。东汉儒林传。云小序是卫宏作。而朱子以为亦不是卫宏作。是二三人手而合成一序者。盖以其零凑附会也。卫宏犹不为则况子夏乎。朱子之论。至此益严。而小序于是乎废矣。近见一文字。自燕中出来者。载其论诗说而曰。汉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之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则得之赵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于卜氏子夏。子夏亲见圣人者。总其删述之旨。为之序论。以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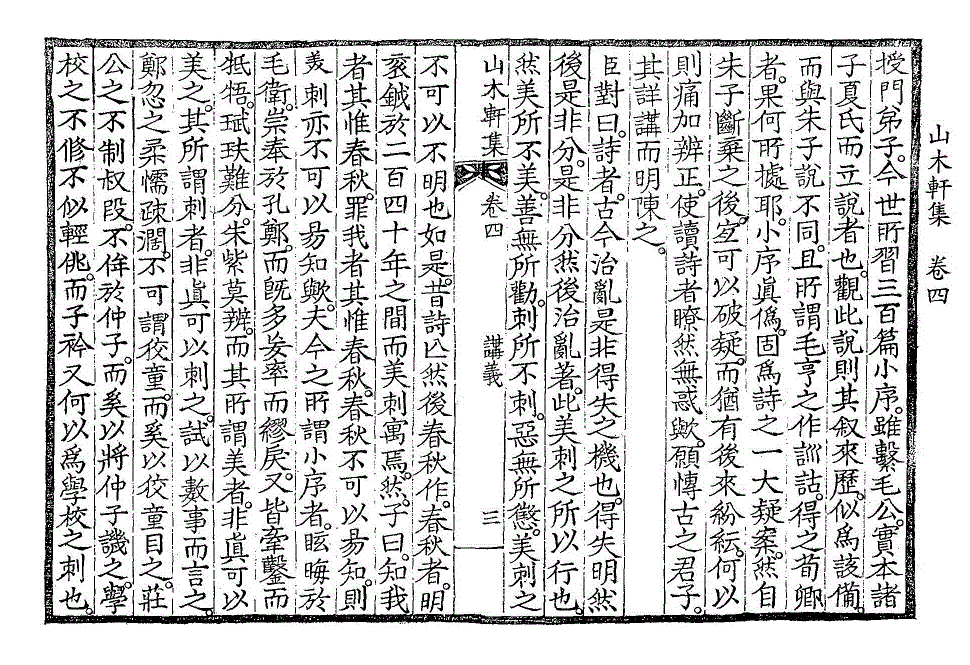 授门弟子。今世所习三百篇小序。虽系毛公。实本诸子夏氏而立说者也。观此说则其叙来历。似为该备。而与朱子说不同。且所谓毛亨之作训诂。得之荀卿者。果何所据耶。小序真伪。固为诗之一大疑案。然自朱子断弃之后。宜可以破疑。而犹有后来纷纭。何以则痛加辨正。使读诗者瞭然无惑欤。愿博古之君子。其详讲而明陈之。
授门弟子。今世所习三百篇小序。虽系毛公。实本诸子夏氏而立说者也。观此说则其叙来历。似为该备。而与朱子说不同。且所谓毛亨之作训诂。得之荀卿者。果何所据耶。小序真伪。固为诗之一大疑案。然自朱子断弃之后。宜可以破疑。而犹有后来纷纭。何以则痛加辨正。使读诗者瞭然无惑欤。愿博古之君子。其详讲而明陈之。臣对曰。诗者。古今治乱是非得失之机也。得失明然后是非分。是非分然后治乱著。此美刺之所以行也。然美所不美。善无所劝。刺所不刺。恶无所惩。美刺之不可以不明也如是。昔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者。明衮钺于二百四十年之间而美刺寓焉。然。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春秋不可以易知。则美刺亦不可以易知欤。夫今之所谓小序者。眩晦于毛卫。崇奉于孔郑。而既多妄率而缪戾。又皆牵凿而牴牾。珷玞难分。朱紫莫辨。而其所谓美者。非真可以美之。其所谓刺者。非真可以刺之。试以数事而言之。郑忽之柔懦疏阔。不可谓狡童。而奚以狡童目之。庄公之不制叔段。不侔于仲子。而奚以将仲子讥之。学校之不修不似轻佻。而子衿又何以为学校之刺也。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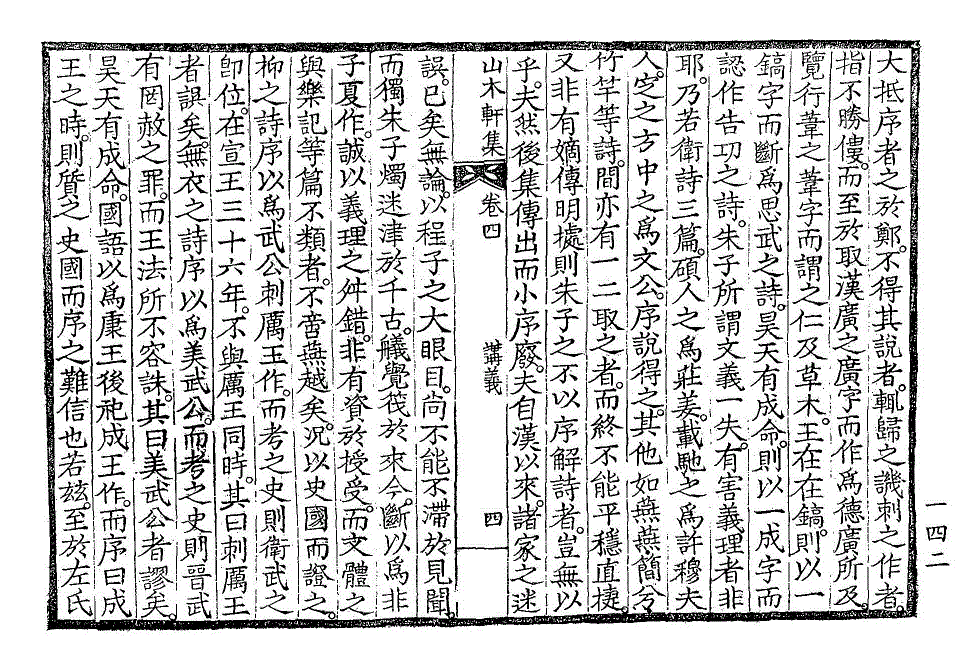 大抵序者之于郑。不得其说者。辄归之讥刺之作者。指不胜偻。而至于取汉广之广字而作为德广所及。览行苇之苇字而谓之仁及草木。王在在镐。则以一镐字而断为思武之诗。昊天有成命。则以一成字而认作告功之诗。朱子所谓文义一失。有害义理者非耶。乃若卫诗三篇。硕人之为庄姜。载驰之为许穆夫人。定之方中之为文公。序说得之。其他如燕燕,简兮,竹竿等诗。间亦有一二取之者。而终不能平稳直捷。又非有嫡传明据则朱子之不以序解诗者。岂无以乎。夫然后集传出而小序废。夫自汉以来。诸家之迷误。已矣无论。以程子之大眼目。尚不能不滞于见闻。而独朱子烛迷津于千古。舣觉筏于来今。断以为非子夏作。诚以义理之舛错。非有资于授受。而文体之与乐记等篇不类者。不啻燕越矣。况以史国而證之。抑之诗序以为武公刺厉王作。而考之史则卫武之即位。在宣王三十六年。不与厉王同时。其曰刺厉王者误矣。无衣之诗序以为美武公。而考之史则晋武有罔赦之罪。而王法所不容诛。其曰美武公者谬矣。昊天有成命。国语以为康王后祀成王作。而序曰成王之时。则质之史国而序之难信也若玆。至于左氏
大抵序者之于郑。不得其说者。辄归之讥刺之作者。指不胜偻。而至于取汉广之广字而作为德广所及。览行苇之苇字而谓之仁及草木。王在在镐。则以一镐字而断为思武之诗。昊天有成命。则以一成字而认作告功之诗。朱子所谓文义一失。有害义理者非耶。乃若卫诗三篇。硕人之为庄姜。载驰之为许穆夫人。定之方中之为文公。序说得之。其他如燕燕,简兮,竹竿等诗。间亦有一二取之者。而终不能平稳直捷。又非有嫡传明据则朱子之不以序解诗者。岂无以乎。夫然后集传出而小序废。夫自汉以来。诸家之迷误。已矣无论。以程子之大眼目。尚不能不滞于见闻。而独朱子烛迷津于千古。舣觉筏于来今。断以为非子夏作。诚以义理之舛错。非有资于授受。而文体之与乐记等篇不类者。不啻燕越矣。况以史国而證之。抑之诗序以为武公刺厉王作。而考之史则卫武之即位。在宣王三十六年。不与厉王同时。其曰刺厉王者误矣。无衣之诗序以为美武公。而考之史则晋武有罔赦之罪。而王法所不容诛。其曰美武公者谬矣。昊天有成命。国语以为康王后祀成王作。而序曰成王之时。则质之史国而序之难信也若玆。至于左氏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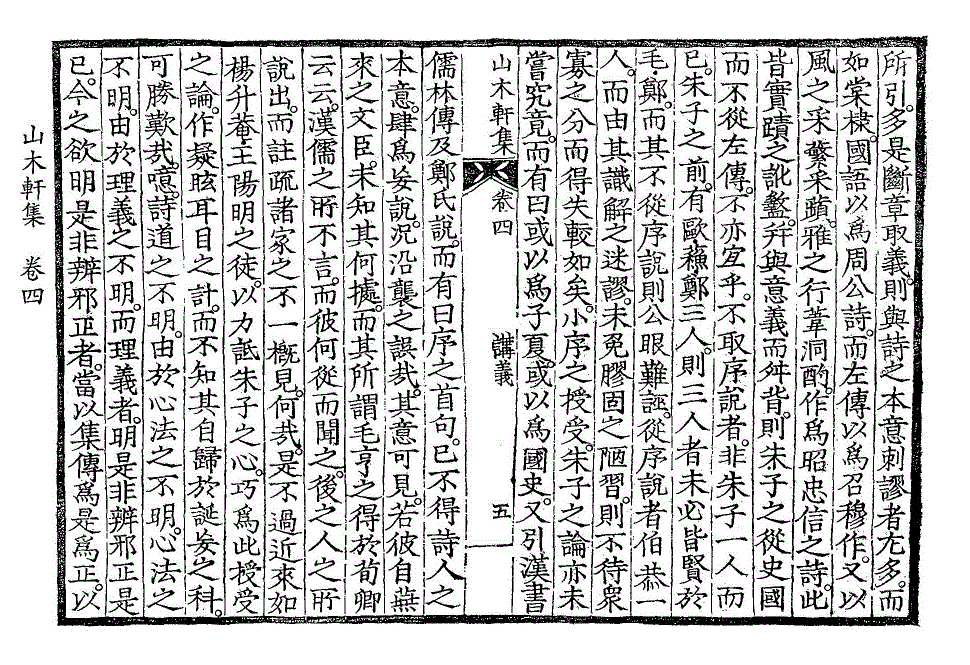 所引。多是断章取义。则与诗之本意刺谬者尤多。而如棠棣。国语以为周公诗。而左传以为召穆作。又以风之采蘩采蘋。雅之行苇洞酌。作为昭忠信之诗。此皆实迹之讹盭。并与意义而舛背。则朱子之从史国而不从左传。不亦宜乎。不取序说者。非朱子一人而已。朱子之前。有欧,苏,郑三人。则三人者未必皆贤于毛,郑。而其不从序说则公眼难诬。从序说者伯恭一人。而由其识解之迷谬。未免胶固之陋习。则不待众寡之分而得失较如矣。小序之授受。朱子之论亦未尝究竟。而有曰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又引汉书儒林传及郑氏说。而有曰序之首句。已不得诗人之本意。肆为妄说。况沿袭之误哉。其意可见。若彼自燕来之文臣。未知其何据。而其所谓毛亨之得于荀卿云云。汉儒之所不言。而彼何从而闻之。后之人之所说出。而注疏诸家之不一概见。何哉。是不过近来如杨升庵,王阳明之徒。以力诋朱子之心。巧为此授受之论。作疑眩耳目之计。而不知其自归于诞妄之科。可胜叹哉。噫。诗道之不明。由于心法之不明。心法之不明。由于理义之不明。而理义者。明是非辨邪正是已。今之欲明是非辨邪正者。当以集传为是为正。以
所引。多是断章取义。则与诗之本意刺谬者尤多。而如棠棣。国语以为周公诗。而左传以为召穆作。又以风之采蘩采蘋。雅之行苇洞酌。作为昭忠信之诗。此皆实迹之讹盭。并与意义而舛背。则朱子之从史国而不从左传。不亦宜乎。不取序说者。非朱子一人而已。朱子之前。有欧,苏,郑三人。则三人者未必皆贤于毛,郑。而其不从序说则公眼难诬。从序说者伯恭一人。而由其识解之迷谬。未免胶固之陋习。则不待众寡之分而得失较如矣。小序之授受。朱子之论亦未尝究竟。而有曰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又引汉书儒林传及郑氏说。而有曰序之首句。已不得诗人之本意。肆为妄说。况沿袭之误哉。其意可见。若彼自燕来之文臣。未知其何据。而其所谓毛亨之得于荀卿云云。汉儒之所不言。而彼何从而闻之。后之人之所说出。而注疏诸家之不一概见。何哉。是不过近来如杨升庵,王阳明之徒。以力诋朱子之心。巧为此授受之论。作疑眩耳目之计。而不知其自归于诞妄之科。可胜叹哉。噫。诗道之不明。由于心法之不明。心法之不明。由于理义之不明。而理义者。明是非辨邪正是已。今之欲明是非辨邪正者。当以集传为是为正。以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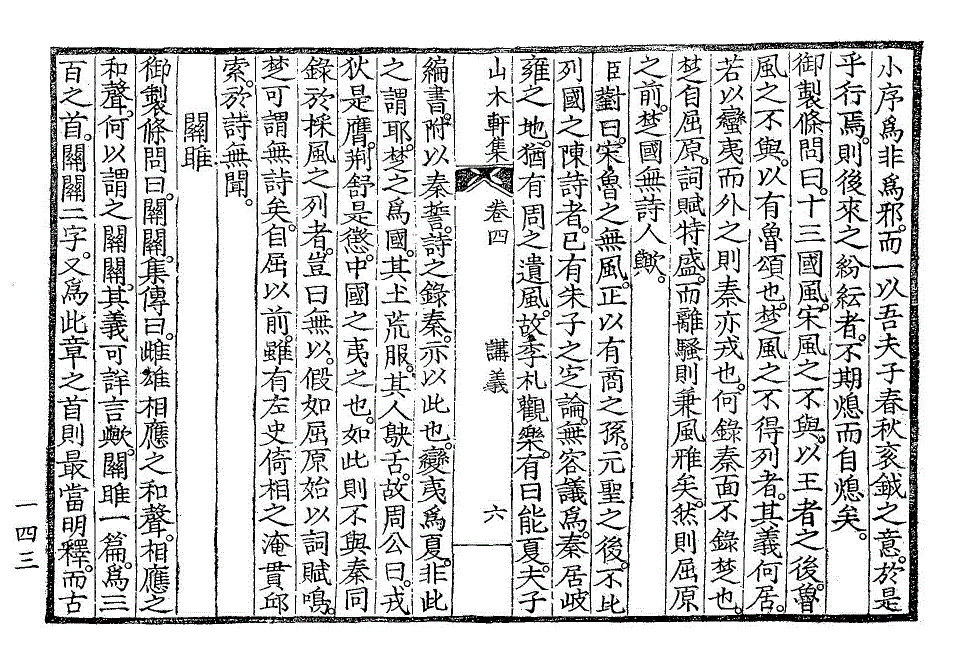 小序为非为邪。而一以吾夫子春秋衮钺之意。于是乎行焉。则后来之纷纭者。不期熄而自熄矣。
小序为非为邪。而一以吾夫子春秋衮钺之意。于是乎行焉。则后来之纷纭者。不期熄而自熄矣。御制条问曰。十三国风。宋风之不与。以王者之后。鲁风之不与。以有鲁颂也。楚风之不得列者。其义何居。若以蛮夷而外之则秦亦戎也。何录秦面不录楚也。楚自屈原。词赋特盛。而离骚则兼风雅矣。然则屈原之前。楚国无诗人欤。
臣对曰。宋,鲁之无风。正以有商之孙。元圣之后。不比列国之陈诗者。已有朱子之定论。无容议为。秦居岐雍之地。犹有周之遗风。故季札观乐。有曰能夏。夫子编书。附以秦誓。诗之录秦。亦以此也。变夷为夏。非此之谓耶。楚之为国。其土荒服。其人鴃舌。故周公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中国之夷之也。如此则不与秦同录于采风之列者。岂曰无以。假如屈原始以词赋鸣。楚可谓无诗矣。自屈以前。虽有左史倚相之淹贯邱索。于诗无闻。
[周南]
关雎
御制条问曰。关关。集传曰。雌雄相应之和声。相应之和声。何以谓之关关。其义可详言欤。关雎一篇。为三百之首。关关二字。又为此章之首则最当明释。而古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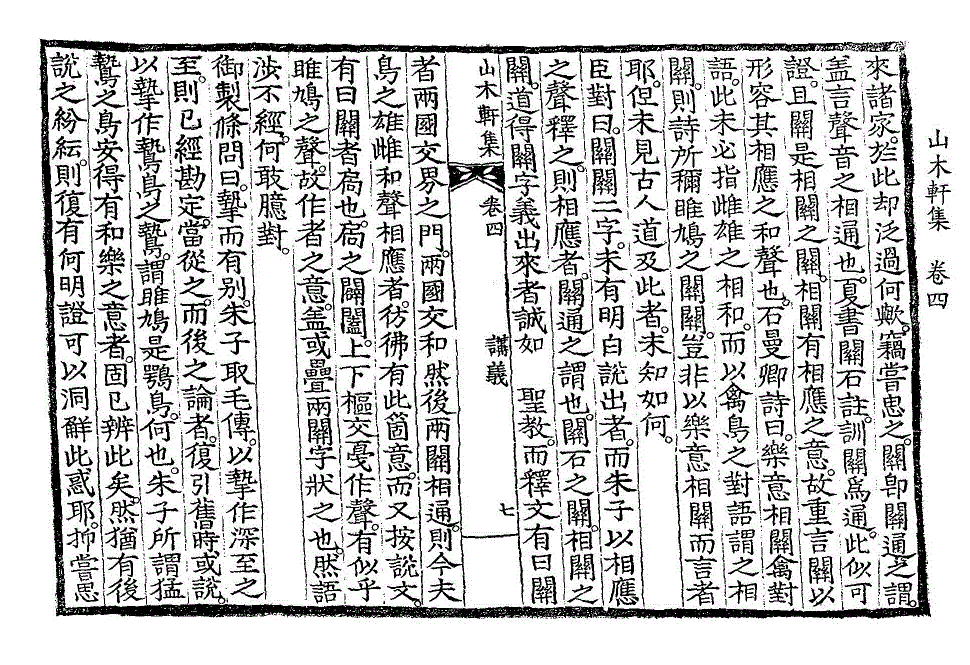 来诸家。于此却泛过何欤。窃尝思之。关即关通之谓。盖言声音之相通也。夏书关石注。训关为通。此似可證。且关是相关之关。相关有相应之意。故重言关以形容其相应之和声也。石曼卿诗曰。乐意相关禽对语。此未必指雌雄之相和。而以禽鸟之对语谓之相关。则诗所称雎鸠之关关。岂非以乐意相关而言者耶。但未见古人道及此者。未知如何。
来诸家。于此却泛过何欤。窃尝思之。关即关通之谓。盖言声音之相通也。夏书关石注。训关为通。此似可證。且关是相关之关。相关有相应之意。故重言关以形容其相应之和声也。石曼卿诗曰。乐意相关禽对语。此未必指雌雄之相和。而以禽鸟之对语谓之相关。则诗所称雎鸠之关关。岂非以乐意相关而言者耶。但未见古人道及此者。未知如何。臣对曰。关关二字。未有明白说出者。而朱子以相应之声释之。则相应者。关通之谓也。关石之关。相关之关。道得关字义出来者诚如 圣教。而释文有曰关者两国交界之门。两国交和然后两关相通。则今夫鸟之雄雌和声相应者。彷佛有此个意。而又按说文。有曰关者扃也。扃之辟阖。上下枢交戛作声。有似乎雎鸠之声。故作者之意。盖或叠两关字状之也。然语涉不经。何敢臆对。
御制条问曰。挚而有别。朱子取毛传。以挚作深至之至。则已经勘定。当从之。而后之论者。复引旧时或说。以挚作鸷鸟之鸷。谓雎鸠是鹗鸟。何也。朱子所谓猛鸷之鸟安得有和乐之意者。固已辨此矣。然犹有后说之纷纭。则复有何明證可以洞解此惑耶。抑尝思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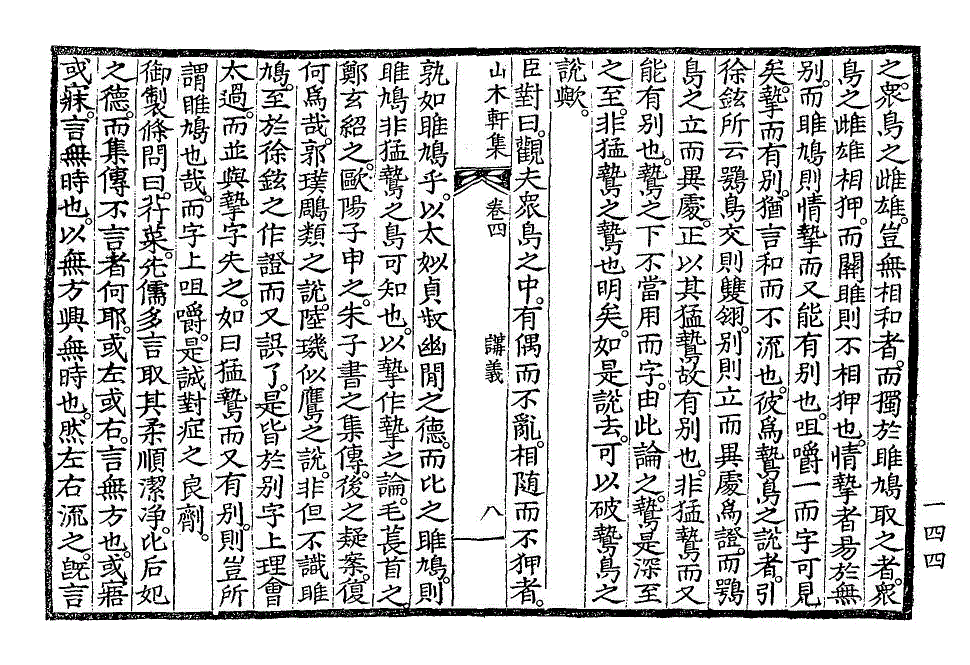 之。众鸟之雌雄。岂无相和者。而独于雎鸠取之者。众鸟之雌雄相狎。而关雎则不相狎也。情挚者易于无别。而雎鸠则情挚而又能有别也。咀嚼一而字可见矣。挚而有别。犹言和而不流也。彼为鸷鸟之说者。引徐铉所云鹗鸟交则双翎。别则立而异处为證。而鹗鸟之立而异处。正以其猛鸷故有别也。非猛鸷而又能有别也。鸷之下不当用而字。由此论之。鸷是深至之至。非猛鸷之鸷也明矣。如是说去。可以破鸷鸟之说欤。
之。众鸟之雌雄。岂无相和者。而独于雎鸠取之者。众鸟之雌雄相狎。而关雎则不相狎也。情挚者易于无别。而雎鸠则情挚而又能有别也。咀嚼一而字可见矣。挚而有别。犹言和而不流也。彼为鸷鸟之说者。引徐铉所云鹗鸟交则双翎。别则立而异处为證。而鹗鸟之立而异处。正以其猛鸷故有别也。非猛鸷而又能有别也。鸷之下不当用而字。由此论之。鸷是深至之至。非猛鸷之鸷也明矣。如是说去。可以破鸷鸟之说欤。臣对曰。观夫众鸟之中。有偶而不乱。相随而不狎者。孰如雎鸠乎。以太姒贞叔幽閒之德。而比之雎鸠。则雎鸠非猛鸷之鸟可知也。以挚作挚之论。毛苌首之。郑玄绍之。欧阳子申之。朱子书之集传。后之疑案。复何为哉。郭璞雕类之说。陆玑似鹰之说。非但不识雎鸠。至于徐铉之作證而又误了。是皆于别字上理会太过。而并与挚字失之。如曰猛鸷而又有别。则岂所谓雎鸠也哉。而字上咀嚼。是诚对症之良剂。
御制条问曰。荇菜。先儒多言取其柔顺洁净。比后妃之德。而集传不言者何耶。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或寤或寐。言无时也。以无方兴无时也。然左右流之。既言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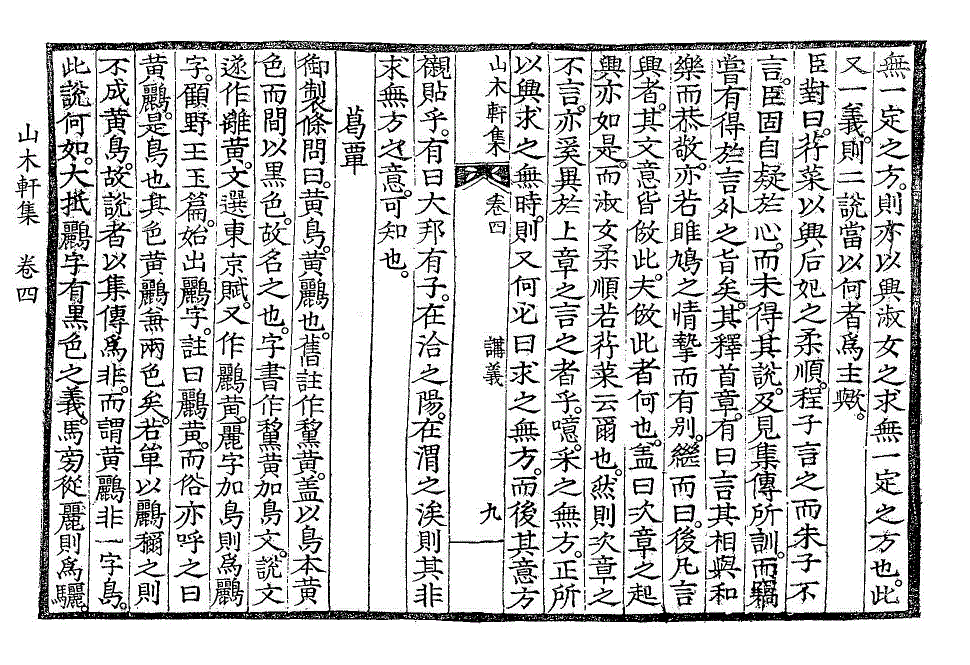 无一定之方。则亦以兴淑女之求无一定之方也。此又一义。则二说当以何者为主欤。
无一定之方。则亦以兴淑女之求无一定之方也。此又一义。则二说当以何者为主欤。臣对曰。荇菜以兴后妃之柔顺。程子言之而朱子不言。臣固自疑于心。而未得其说。及见集传所训。而窃尝有得于言外之旨矣。其释首章。有曰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继而曰。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仿此。夫仿此者何也。盖曰次章之起兴亦如是。而淑女柔顺若荇菜云尔也。然则次章之不言。亦奚异于上章之言之者乎。噫。采之无方。正所以兴求之无时。则又何必曰求之无方。而后其意方衬贴乎。有曰大邦有子。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则其非求无方之意。可知也。
葛覃
御制条问曰。黄鸟。黄鹂也。旧注作黧黄。盖以鸟本黄色而间以黑色。故名之也。字书作黧黄加鸟文。说文遂作离黄。文选东京赋。又作鹂黄。丽字加鸟则为鹂字。顾野王玉篇。始出鹂字。注曰鹂黄。而俗亦呼之曰黄鹂。是鸟也其色黄鹂兼两色矣。若单以鹂称之则不成黄鸟。故说者以集传为非。而谓黄鹂非一字鸟。此说何如。大抵鹂字有黑色之义。马旁从丽则为骊。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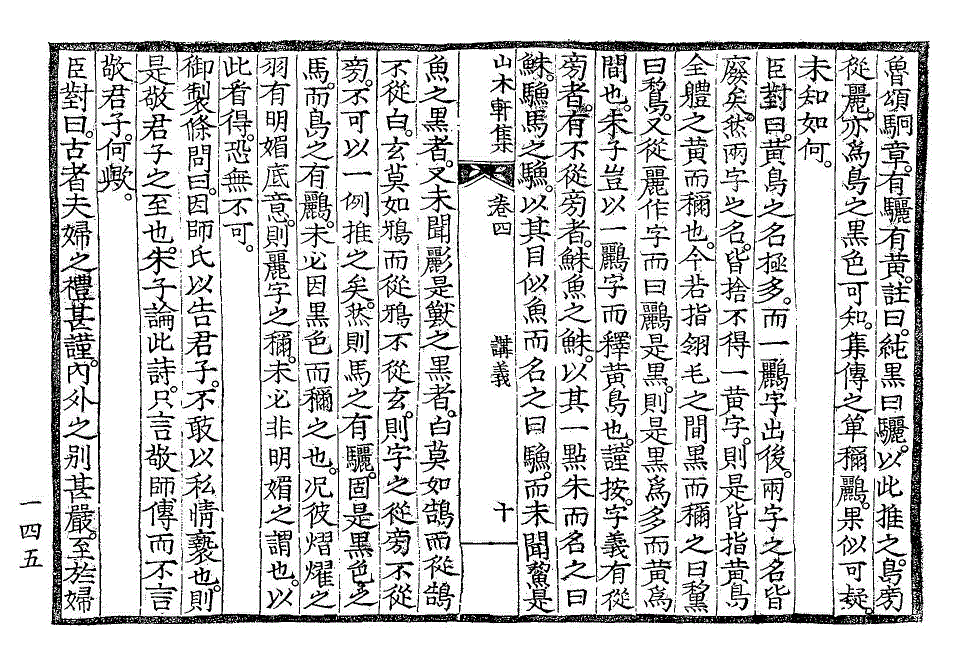 鲁颂駉章。有骊有黄。注曰。纯黑曰骊。以此推之。鸟旁从丽。亦为鸟之黑色可知。集传之单称鹂。果似可疑。未知如何。
鲁颂駉章。有骊有黄。注曰。纯黑曰骊。以此推之。鸟旁从丽。亦为鸟之黑色可知。集传之单称鹂。果似可疑。未知如何。臣对曰。黄鸟之名极多。而一鹂字出后。两字之名皆废矣。然两字之名。皆舍不得一黄字。则是皆指黄鸟全体之黄而称也。今若指翎毛之间黑而称之曰黧曰鵹。又从丽作字而曰鹂是黑。则是黑为多而黄为间也。朱子岂以一鹂字而释黄鸟也。谨按。字义有从旁者。有不从旁者。鮢鱼之鮢。以其一点朱而名之曰鮢。𩥭马之𩥭。以其目似鱼而名之曰𩥭。而未闻鯬是鱼之黑者。又未闻螭是兽之黑者。白莫如鹄而从鹄不从白。玄莫如鸦而从鸦不从玄。则字之从旁不从旁。不可以一例推之矣。然则马之有骊。固是黑色之马。而鸟之有鹂。未必因黑色而称之也。况彼熠耀之羽有明媚底意。则丽字之称。未必非明媚之谓也。以此看得。恐无不可。
御制条问曰。因师氏以告君子。不敢以私情亵也。则是敬君子之至也。朱子论此诗。只言敬师傅而不言敬君子。何欤。
臣对曰。古者夫妇之礼甚谨。内外之别甚严。至于妇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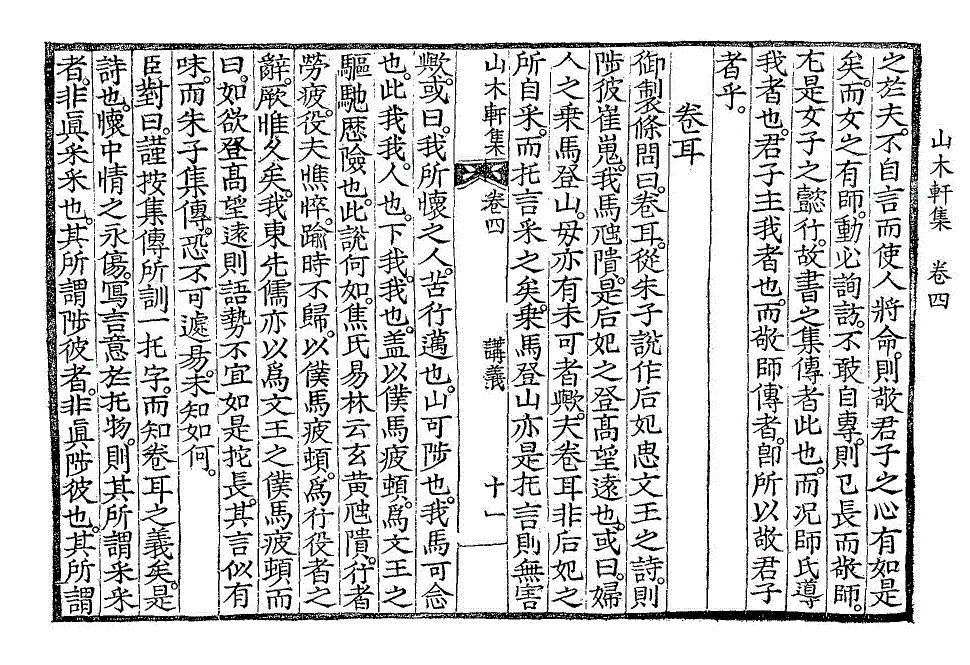 之于夫。不自言而使人将命。则敬君子之心有如是矣。而女之有师。动必询访。不敢自专。则已长而敬师。尤是女子之懿行。故书之集传者此也。而况师氏导我者也。君子主我者也。而敬师傅者。即所以敬君子者乎。
之于夫。不自言而使人将命。则敬君子之心有如是矣。而女之有师。动必询访。不敢自专。则已长而敬师。尤是女子之懿行。故书之集传者此也。而况师氏导我者也。君子主我者也。而敬师傅者。即所以敬君子者乎。卷耳
御制条问曰。卷耳。从朱子说作后妃思文王之诗。则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是后妃之登高望远也。或曰。妇人之乘马登山。毋亦有未可者欤。夫卷耳非后妃之所自采。而托言采之矣。乘马登山亦是托言则无害欤。或曰。我所怀之人。苦行迈也。山可陟也。我马可念也。此我。我人也。下我。我也。盖以仆马疲顿。为文王之驱驰历险也。此说何如。焦氏易林云玄黄虺隤。行者劳疲。役夫憔悴。踰时不归。以仆马疲顿。为行役者之辞。厥惟久矣。我东先儒亦以为文王之仆马疲顿而曰。如欲登高望远则语势不宜如是拖长。其言似有味。而朱子集传。恐不可遽易。未知如何。
臣对曰。谨按集传所训一托字。而知卷耳之义矣。是诗也。怀中情之永伤。写言意于托物。则其所谓采采者。非真采采也。其所谓陟彼者。非真陟彼也。其所谓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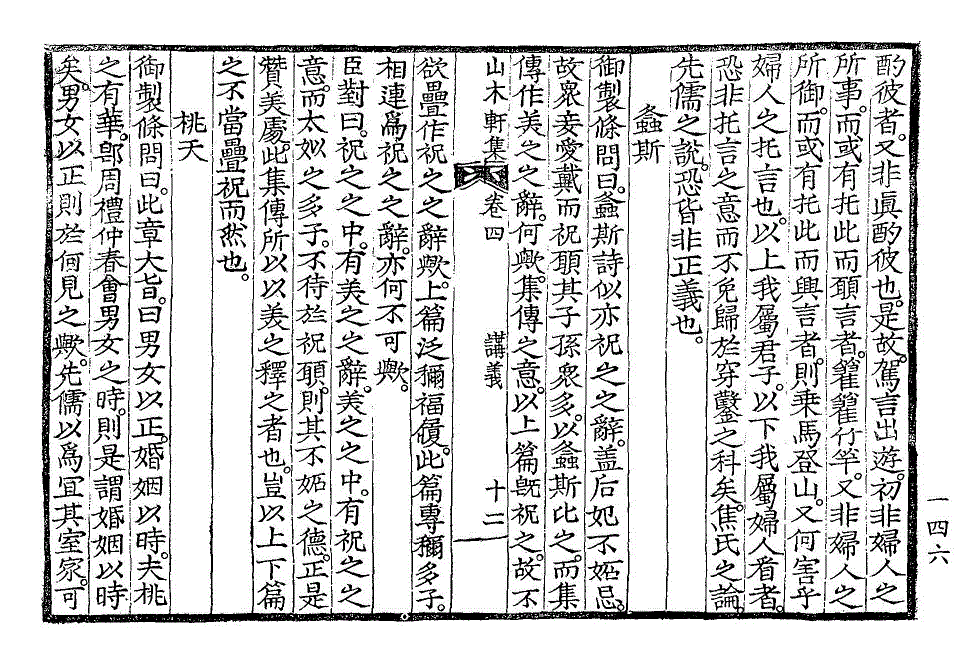 酌彼者。又非真酌彼也。是故。驾言出游。初非妇人之所事。而或有托此而愿言者。籊籊竹竿。又非妇人之所御。而或有托此而兴言者。则乘马登山。又何害乎妇人之托言也。以上我属君子。以下我属妇人看者。恐非托言之意而不免归于穿凿之科矣。焦氏之论。先儒之说。恐皆非正义也。
酌彼者。又非真酌彼也。是故。驾言出游。初非妇人之所事。而或有托此而愿言者。籊籊竹竿。又非妇人之所御。而或有托此而兴言者。则乘马登山。又何害乎妇人之托言也。以上我属君子。以下我属妇人看者。恐非托言之意而不免归于穿凿之科矣。焦氏之论。先儒之说。恐皆非正义也。螽斯
御制条问曰。螽斯诗似亦祝之之辞。盖后妃不妒忌。故众妾爱戴而祝愿其子孙众多。以螽斯比之。而集传作美之之辞。何欤。集传之意。以上篇既祝之。故不欲叠作祝之之辞欤。上篇泛称福履。此篇专称多子。相连为祝之之辞。亦何不可欤。
臣对曰。祝之之中。有美之之辞。美之之中。有祝之之意。而太姒之多子。不待于祝愿。则其不妒之德。正是赞美处。此集传所以以美之释之者也。岂以上下篇之不当叠祝而然也。
桃夭
御制条问曰。此章大旨。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夫桃之有华。即周礼仲春会男女之时。则是谓婚姻以时矣。男女以正则于何见之欤。先儒以为宜其室家。可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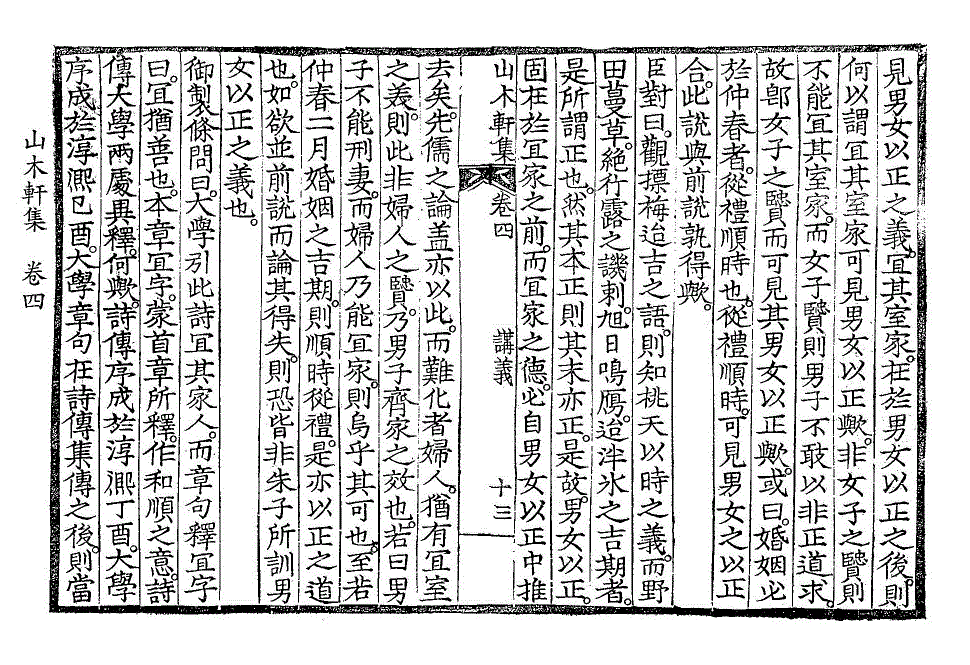 见男女以正之义。宜其室家。在于男女以正之后。则何以谓宜其室家可见男女以正欤。非女子之贤则不能宜其室家。而女子贤则男子不敢以非正道求。故即女子之贤而可见其男女以正欤。或曰。婚姻必于仲春者。从礼顺时也。从礼顺时。可见男女之以正合。此说与前说孰得欤。
见男女以正之义。宜其室家。在于男女以正之后。则何以谓宜其室家可见男女以正欤。非女子之贤则不能宜其室家。而女子贤则男子不敢以非正道求。故即女子之贤而可见其男女以正欤。或曰。婚姻必于仲春者。从礼顺时也。从礼顺时。可见男女之以正合。此说与前说孰得欤。臣对曰。观摽梅迨吉之语。则知桃夭以时之义。而野田蔓草。绝行露之讥刺。旭日鸣雁。迨泮冰之吉期者。是所谓正也。然其本正则其末亦正。是故。男女以正。固在于宜家之前。而宜家之德。必自男女以正中推去矣。先儒之论盖亦以此。而难化者妇人。犹有宜室之美。则此非妇人之贤。乃男子齐家之效也。若曰男子不能刑妻。而妇人乃能宜家。则乌乎其可也。至若仲春二月婚姻之吉期。则顺时从礼。是亦以正之道也。如欲并前说而论其得失。则恐皆非朱子所训男女以正之义也。
御制条问曰。大学引此诗宜其家人。而章句释宜字曰。宜犹善也。本章宜字。蒙首章所释。作和顺之意。诗传,大学两处异释。何欤。诗传序成于淳熙丁酉。大学序成于淳熙己酉。大学章句在诗传集传之后。则当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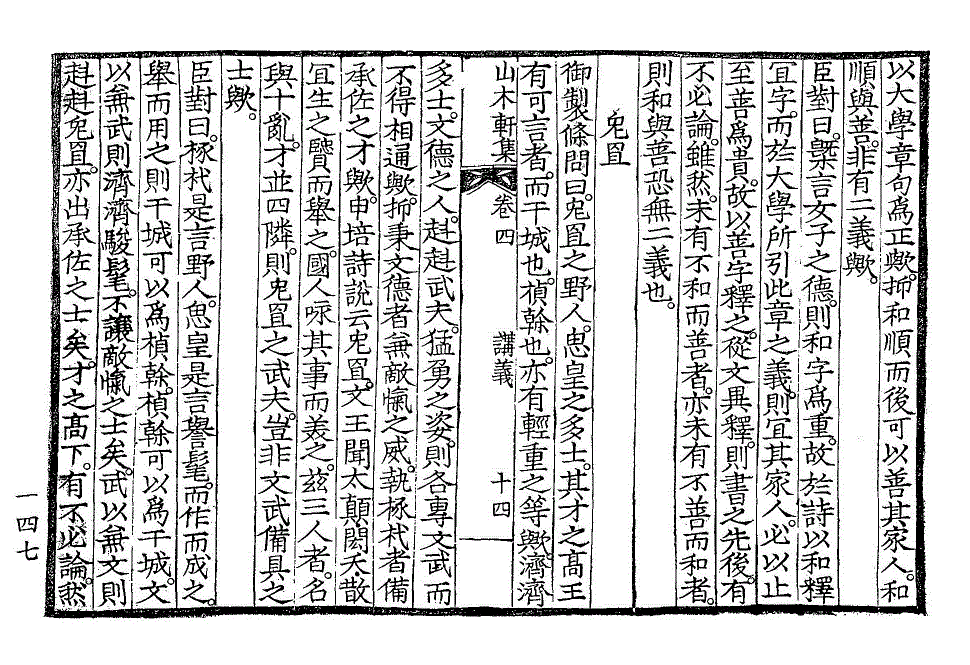 以大学章句为正欤。抑和顺而后可以善其家人。和顺与善。非有二义欤。
以大学章句为正欤。抑和顺而后可以善其家人。和顺与善。非有二义欤。臣对曰。槩言女子之德。则和字为重。故于诗以和释宜字。而于大学所引此章之义。则宜其家人。必以止至善为贵。故以善字释之。从文异释。则书之先后。有不必论。虽然。未有不和而善者。亦未有不善而和者。则和与善恐无二义也。
兔罝
御制条问曰。兔罝之野人。思皇之多士。其才之高王(一作下)有可言者。而干城也。桢干也。亦有轻重之等欤。济济多士。文德之人。赳赳武夫。猛勇之姿。则各专文武而不得相通欤。抑秉文德者兼敌忾之威。执椓杙者备承佐之才欤。申培诗说云兔罝。文王闻太颠,闳夭,散宜生之贤而举之。国人咏其事而美之。玆三人者。名与十乱。才并四邻。则兔罝之武夫。岂非文武备具之士欤。
臣对曰。椓杙是言野人。思皇是言誉髦。而作而成之。举而用之则干城可以为桢干。桢干可以为干城。文以兼武则济济骏髦。不让敌忾之士矣。武以兼文则赳赳兔罝。亦出承佐之士矣。才之高下。有不必论。然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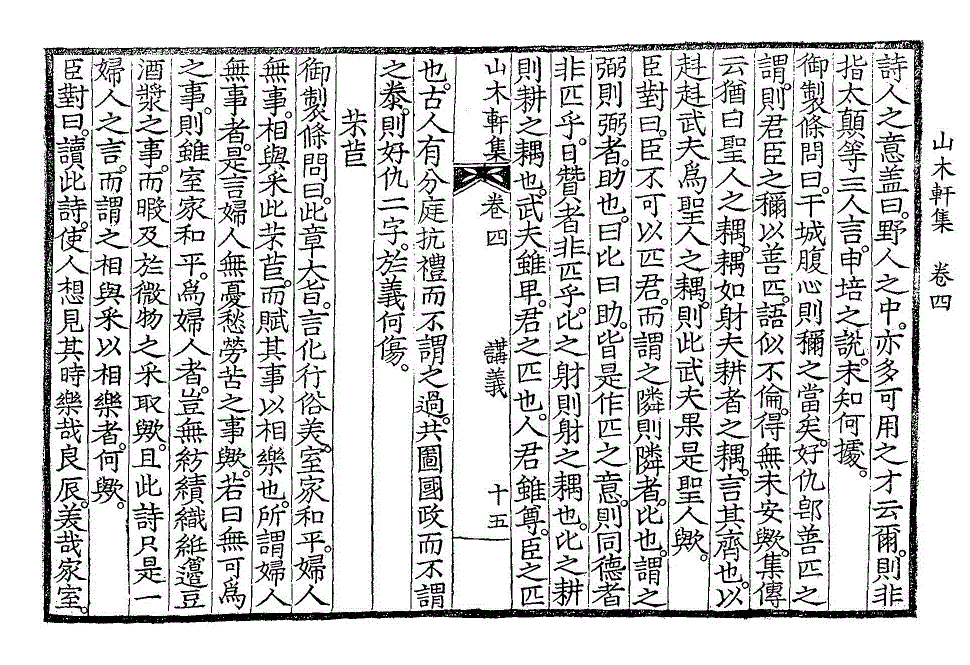 诗人之意盖曰。野人之中。亦多可用之才云尔。则非指太颠等三人言。申培之说。未知何据。
诗人之意盖曰。野人之中。亦多可用之才云尔。则非指太颠等三人言。申培之说。未知何据。御制条问曰。干城腹心则称之当矣。好仇即善匹之谓。则君臣之称以善匹。语似不伦。得无未安欤。集传云犹曰圣人之耦。耦如射夫耕者之耦。言其齐也。以赳赳武夫为圣人之耦。则此武夫果是圣人欤。
臣对曰。臣不可以匹君。而谓之邻则邻者。比也。谓之弼则弼者。助也。曰比曰助。皆是作匹之意。则同德者非匹乎。日赞者非匹乎。比之射则射之耦也。比之耕则耕之耦也。武夫虽卑。君之匹也。人君虽尊。臣之匹也。古人有分庭抗礼而不谓之过。共图国政而不谓之泰。则好仇二字。于义何伤。
芣苣
御制条问曰。此章大旨。言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苣。而赋其事以相乐也。所谓妇人无事者。是言妇人无忧愁劳苦之事欤。若曰无可为之事。则虽室家和平。为妇人者。岂无纺绩织纴笾豆酒浆之事。而暇及于微物之采取欤。且此诗只是一妇人之言。而谓之相与采以相乐者。何欤。
臣对曰。读此诗。使人想见其时乐哉良辰。美哉家室。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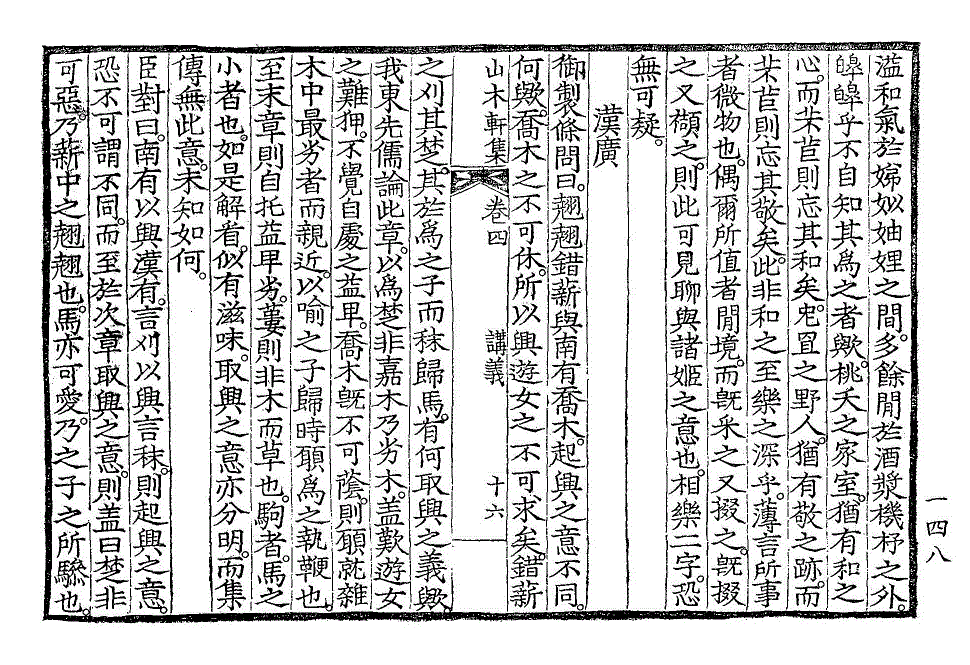 溢和气于娣姒妯娌之间。多馀閒于酒浆机杼之外。皞皞乎不自知其为之者欤。桃夭之家室。犹有和之心。而芣苣则忘其和矣。兔罝之野人。犹有敬之迹。而芣苣则忘其敬矣。此非和之至乐之深乎。薄言所事者微物也。偶尔所值者閒境。而既采之又掇之。既掇之又襭之。则此可见聊与诸姬之意也。相乐二字。恐无可疑。
溢和气于娣姒妯娌之间。多馀閒于酒浆机杼之外。皞皞乎不自知其为之者欤。桃夭之家室。犹有和之心。而芣苣则忘其和矣。兔罝之野人。犹有敬之迹。而芣苣则忘其敬矣。此非和之至乐之深乎。薄言所事者微物也。偶尔所值者閒境。而既采之又掇之。既掇之又襭之。则此可见聊与诸姬之意也。相乐二字。恐无可疑。汉广
御制条问曰。翘翘错薪与南有乔木。起兴之意不同。何欤。乔木之不可休。所以兴游女之不可求矣。错薪之刈其楚。其于为之子而秣归马。有何取兴之义欤。我东先儒论此章。以为楚非嘉木乃劣木。盖叹游女之难狎。不觉自处之益卑。乔木既不可荫。则愿就杂木中最劣者而亲近。以喻之子归时愿为之执鞭也。至末章则自托益卑劣。蒌则非木而草也。驹者。马之小者也。如是解看。似有滋味。取兴之意亦分明。而集传无此意。未知如何。
臣对曰。南有以兴汉有。言刈以兴言秣。则起兴之意。恐不可谓不同。而至于次章取兴之意。则盖曰楚非可恶。乃薪中之翘翘也。马亦可爱。乃之子之所骖也。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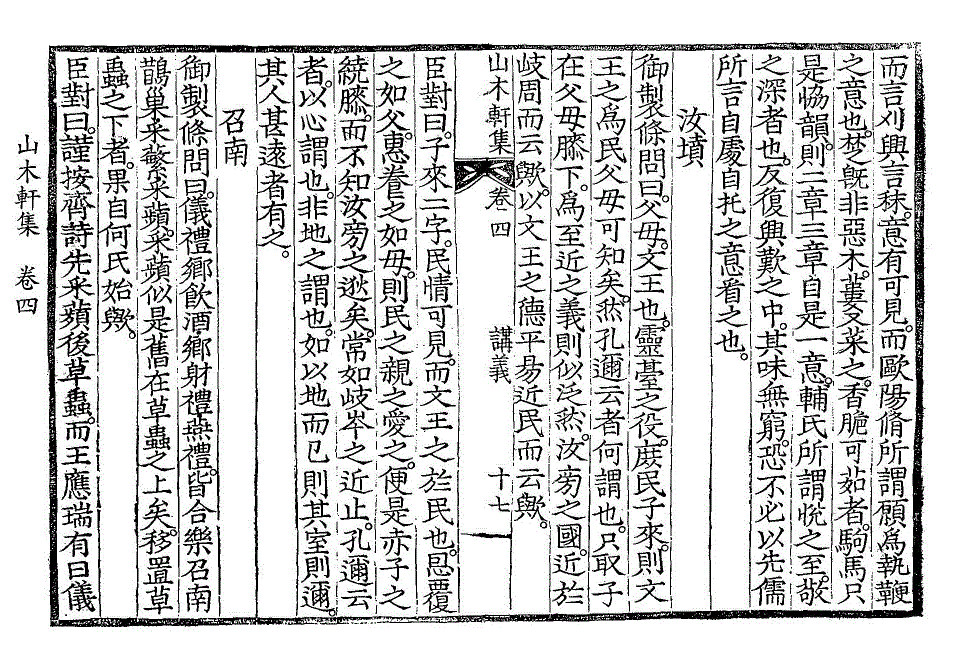 而言刈兴言秣。意有可见。而欧阳脩所谓愿为执鞭之意也。楚既非恶木。蒌又菜之。香脆可茹者。驹马只是协韵。则二章三章自是一意。辅氏所谓悦之至。敬之深者也。反复兴叹之中。其味无穷。恐不必以先儒所言自处自托之意看之也。
而言刈兴言秣。意有可见。而欧阳脩所谓愿为执鞭之意也。楚既非恶木。蒌又菜之。香脆可茹者。驹马只是协韵。则二章三章自是一意。辅氏所谓悦之至。敬之深者也。反复兴叹之中。其味无穷。恐不必以先儒所言自处自托之意看之也。汝坟
御制条问曰。父母。文王也。灵台之役。庶民子来。则文王之为民父母可知矣。然孔迩云者何谓也。只取子在父母膝下。为至近之义则似泛然。汝旁之国。近于岐周而云欤。以文王之德平易近民而云欤。
臣对曰。子来二字。民情可见。而文王之于民也。恩覆之如父。惠养之如母。则民之亲之爱之。便是赤子之绕膝。而不知汝旁之逖矣。常如岐岑之近止。孔迩云者。以心谓也。非地之谓也。如以地而已则其室则迩。其人甚远者有之。
召南
御制条问曰。仪礼乡饮酒,乡射礼,燕礼。皆合乐召南鹊巢,采蘩,采蘋。采蘋似是旧在草虫之上矣。移置草虫之下者。果自何氏始欤。
臣对曰。谨按齐诗先采蘋后草虫。而王应瑞有曰仪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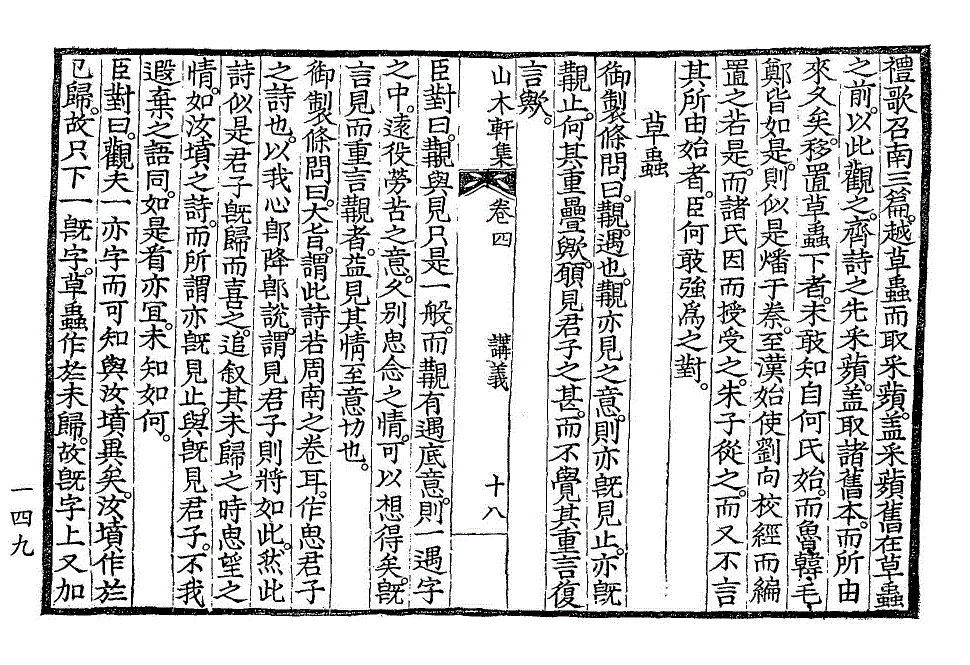 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以此观之。齐诗之先采蘋。盖取诸旧本。而所由来久矣。移置草虫下者。未敢知自何氏始。而鲁,韩,毛,郑皆如是。则似是燔于秦。至汉始使刘向校经而编置之若是。而诸氏因而授受之。朱子从之。而又不言其所由始者。臣何敢强为之对。
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盖采蘋旧在草虫之前。以此观之。齐诗之先采蘋。盖取诸旧本。而所由来久矣。移置草虫下者。未敢知自何氏始。而鲁,韩,毛,郑皆如是。则似是燔于秦。至汉始使刘向校经而编置之若是。而诸氏因而授受之。朱子从之。而又不言其所由始者。臣何敢强为之对。草虫
御制条问曰。觏。遇也。觏亦见之意。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何其重叠欤。愿见君子之甚。而不觉其重言复言欤。
臣对曰。觏与见只是一般。而觏有遇底意。则一遇字之中。远役劳苦之意。久别思念之情。可以想得矣。既言见而重言觏者。益见其情至意切也。
御制条问曰。大旨。谓此诗若周南之卷耳。作思君子之诗也。以我心即降即说。谓见君子则将如此。然此诗似是君子既归而喜之。追叙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汝坟之诗。而所谓亦既见止。与既见君子。不我遐弃之语同。如是看亦宜。未知如何。
臣对曰。观夫一亦字而可知与汝坟异矣。汝坟作于已归。故只下一既字。草虫作于未归。故既字上又加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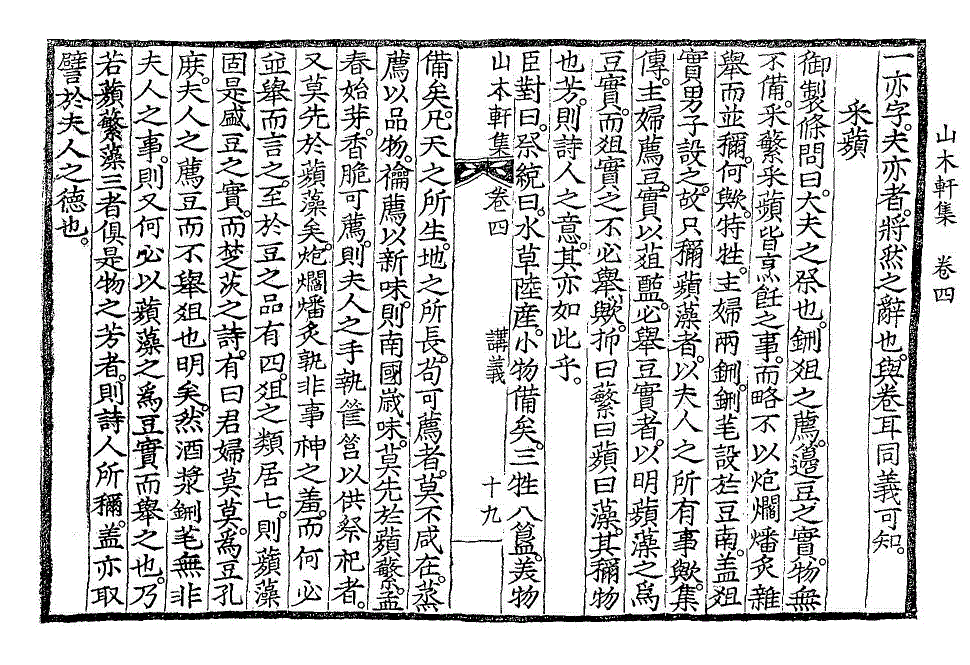 一亦字。夫亦者。将然之辞也。与卷耳同义可知。
一亦字。夫亦者。将然之辞也。与卷耳同义可知。采蘋
御制条问曰。大夫之祭也。铏俎之荐。笾豆之实。物无不备。采蘩采蘋皆烹饪之事。而略不以炮爓燔炙杂举而并称。何欤。特牲。主妇两铏。铏芼设于豆南。盖俎实男子设之。故只称蘋藻者。以夫人之所有事欤。集传。主妇荐豆。实以菹醢。必举豆实者。以明蘋藻之为豆实。而俎实之不必举欤。抑曰蘩曰蘋曰藻。其称物也芳。则诗人之意。其亦如此乎。
臣对曰。祭统曰。水草陆产。小物备矣。三牲八簋。美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蒸荐以品物。礿荐以新味。则南国岁味。莫先于蘋蘩。孟春始芽。香脆可荐。则夫人之手执筐筥以供祭祀者。又莫先于蘋藻矣。炮爓燔炙孰非事神之羞。而何必并举而言之。至于豆之品有四。俎之类居七。则蘋藻固是盛豆之实。而楚茨之诗。有曰君妇莫莫。为豆孔庶。夫人之荐豆而不举俎也明矣。然酒浆铏芼无非夫人之事。则又何必以蘋藻之为豆实而举之也。乃若蘋蘩藻三者俱是物之芳者。则诗人所称。盖亦取譬于夫人之德也。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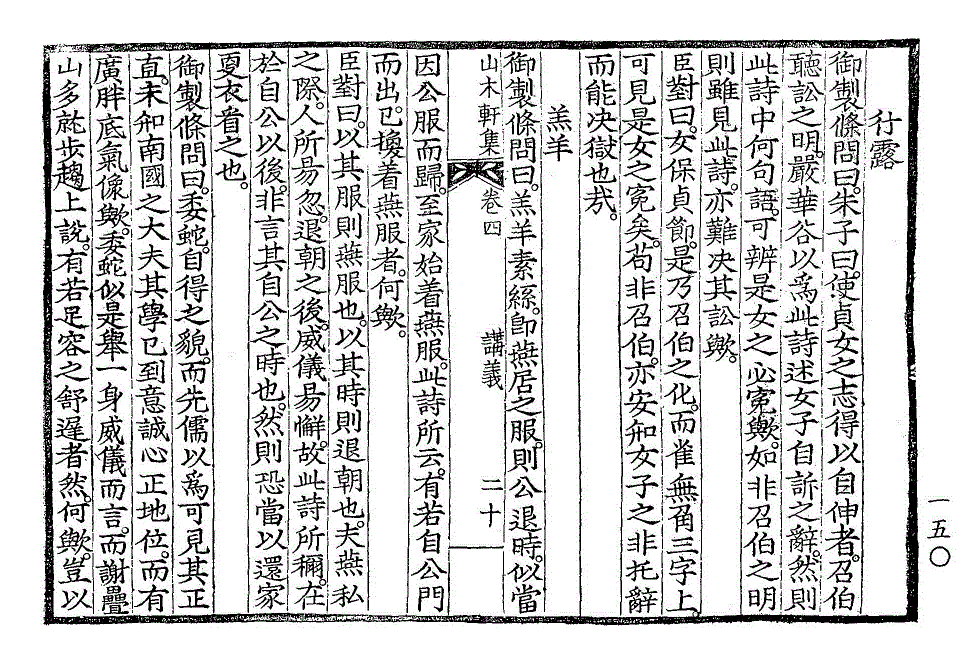 行露
行露御制条问曰。朱子曰。使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听讼之明。严华谷以为此诗述女子自诉之辞。然则此诗中何句语。可辨是女之必冤欤。如非召伯之明则虽见此诗。亦难决其讼欤。
臣对曰。女保贞节。是乃召伯之化。而雀无角三字上。可见是女之冤矣。苟非召伯。亦安知女子之非托辞而能决狱也哉。
羔羊
御制条问曰。羔羊素丝。即燕居之服。则公退时。似当因公服而归。至家始着燕服。此诗所云。有若自公门而出。已换着燕服者。何欤。
臣对曰。以其服则燕服也。以其时则退朝也。夫燕私之际。人所易忽。退朝之后。威仪易懈。故此诗所称。在于自公以后。非言其自公之时也。然则恐当以还家更衣看之也。
御制条问曰。委蛇。自得之貌。而先儒以为可见其正直。未知南国之大夫其学已到意诚心正地位。而有广胖底气像欤。委蛇似是举一身威仪而言。而谢叠山多就步趋上说。有若足容之舒迟者然。何欤。岂以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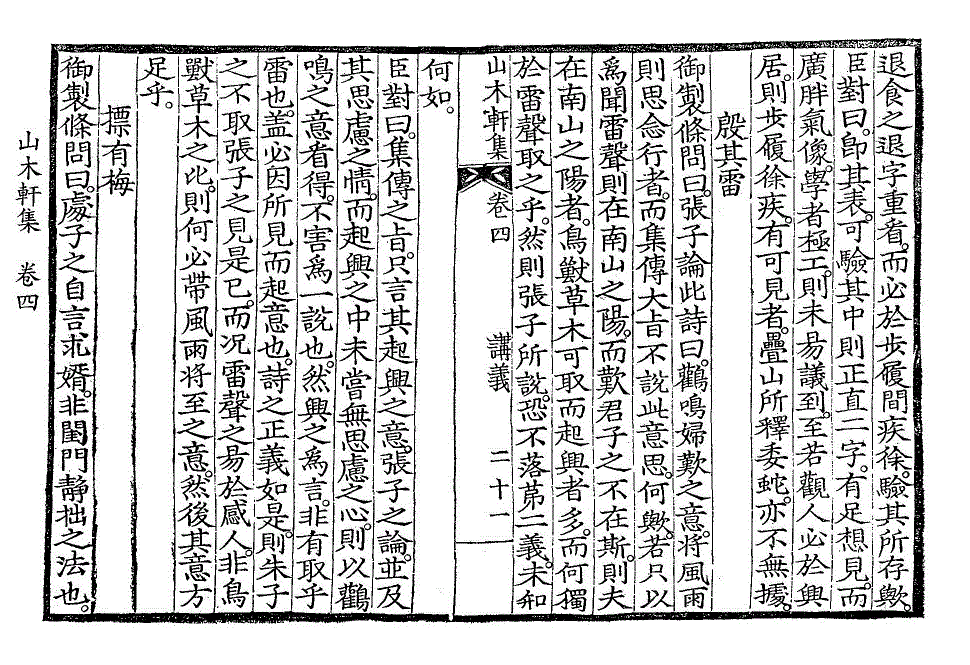 退食之退字重看。而必于步履间疾徐。验其所存欤。
退食之退字重看。而必于步履间疾徐。验其所存欤。臣对曰。即其表。可验其中则正直二字。有足想见。而广胖气像。学者极工。则未易议到。至若观人必于兴居。则步履徐疾。有可见者。叠山所释委蛇。亦不无据。
殷其雷
御制条问曰。张子论此诗曰。鹳鸣妇叹之意。将风雨则思念行者。而集传大旨不说此意思。何欤。若只以为闻雷声则在南山之阳。而叹君子之不在斯。则夫在南山之阳者。鸟兽草木可取而起兴者多。而何独于雷声取之乎。然则张子所说。恐不落第二义。未知何如。
臣对曰。集传之旨。只言其起兴之意。张子之论。并及其思虑之情。而起兴之中未尝无思虑之心。则以鹳鸣之意看得。不害为一说也。然兴之为言。非有取乎雷也。盖必因所见而起意也。诗之正义如是。则朱子之不取张子之见是已。而况雷声之易于感人。非鸟兽草木之比。则何必带风雨将至之意。然后其意方足乎。
摽有梅
御制条问曰。处子之自言求婿。非闺门静拙之法也。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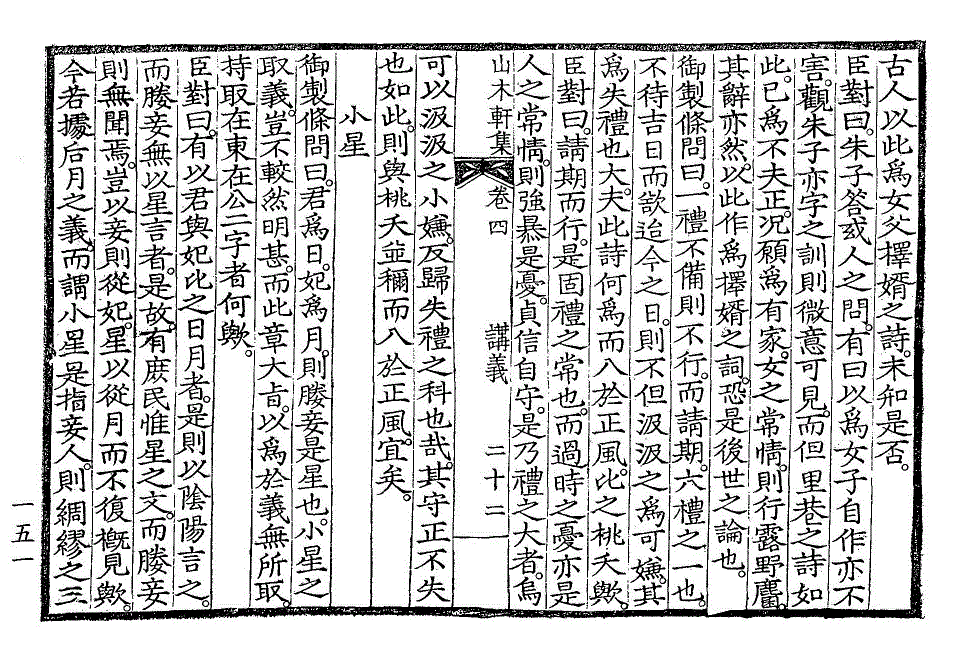 古人以此为女父择婿之诗。未知是否。
古人以此为女父择婿之诗。未知是否。臣对曰。朱子答或人之问。有曰以为女子自作亦不害。观朱子亦字之训则微意可见。而但里巷之诗如此。已为不夫正。况愿为有家。女之常情。则行露野麇。其辞亦然。以此作为择婿之词。恐是后世之论也。
御制条问曰。一礼不备则不行。而请期。六礼之一也。不待吉日而欲迨今之日。则不但汲汲之为可嫌。其为失礼也大。夫此诗何为而入于正风。比之桃夭欤。
臣对曰。请期而行。是固礼之常也。而过时之忧亦是人之常情。则强暴是忧。贞信自守。是乃礼之大者。乌可以汲汲之小嫌。反归失礼之科也哉。其守正不失也如此。则与桃夭并称而入于正风。宜矣。
小星
御制条问曰。君为日。妃为月。则媵妾是星也。小星之取义。岂不较然明甚。而此章大旨。以为于义无所取。持取在东在公二字者何欤。
臣对曰。有以君与妃比之日月者。是则以阴阳言之。而媵妾无以星言者。是故。有庶民惟星之文。而媵妾则无闻焉。岂以妾则从妃。星以从月而不复概见欤。今若据后月之义。而谓小星是指妾人。则绸缪之三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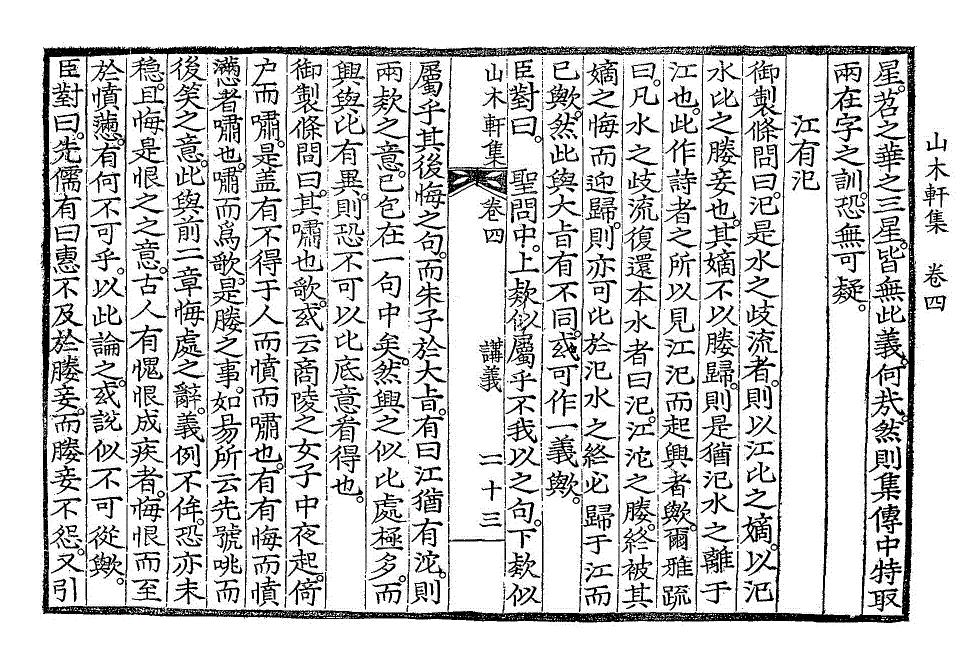 星。苕之华之三星。皆无此义。何哉。然则集传中特取两在字之训。恐无可疑。
星。苕之华之三星。皆无此义。何哉。然则集传中特取两在字之训。恐无可疑。江有汜
御制条问曰。汜是水之歧流者。则以江比之嫡。以汜水比之媵妾也。其嫡不以媵归。则是犹汜水之离于江也。此作诗者之所以见江汜而起兴者欤。尔雅疏曰。凡水之歧流复还本水者曰汜。江沱之媵。终被其嫡之悔而迎归。则亦可比于汜水之终必归于江而已欤。然此与大旨有不同。或可作一义欤。
臣对曰。 圣问中。上款似属乎不我以之句。下款似属乎其后悔之句。而朱子于大旨。有曰江犹有沱。则两款之意。已包在一句中矣。然兴之似比处极多。而兴与比有异。则恐不可以比底意看得也。
御制条问曰。其啸也歌。或云商陵之女子中夜起。倚户而啸。是盖有不得于人而愤而啸也。有有悔而愤懑者啸也。啸而为歌。是媵之事。如易所云先号咷而后笑之意。此与前二章悔处之辞。义例不侔。恐亦未稳。且悔是恨之之意。古人有愧恨成疾者。悔恨而至于愤懑。有何不可乎。以此论之。或说似不可从欤。
臣对曰。先儒有曰惠不及于媵妾。而媵妾不怨。又引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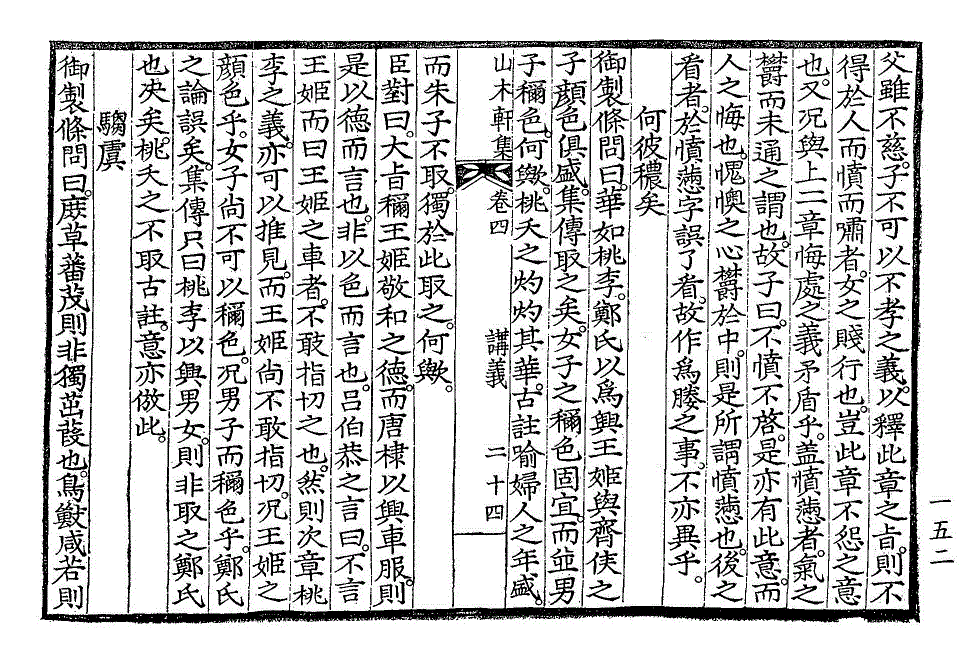 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义。以释此章之旨。则不得于人而愤而啸者。女之贱行也。岂此章不怨之意也。又况与上二章悔处之义矛盾乎。盖愤懑者。气之郁而未通之谓也。故子曰。不愤不启。是亦有此意。而人之悔也。愧懊之心郁于中。则是所谓愤懑也。后之看者。于愤懑字误了看。故作为媵之事。不亦异乎。
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义。以释此章之旨。则不得于人而愤而啸者。女之贱行也。岂此章不怨之意也。又况与上二章悔处之义矛盾乎。盖愤懑者。气之郁而未通之谓也。故子曰。不愤不启。是亦有此意。而人之悔也。愧懊之心郁于中。则是所谓愤懑也。后之看者。于愤懑字误了看。故作为媵之事。不亦异乎。何彼秾矣
御制条问曰。华如桃李。郑氏以为兴王姬与齐侯之子颜色俱盛。集传取之矣。女子之称色固宜。而并男子称色。何欤。桃夭之灼灼其华。古注喻妇人之年盛。而朱子不取。独于此取之。何欤。
臣对曰。大旨称王姬敬和之德。而唐棣以兴车服。则是以德而言也。非以色而言也。吕伯恭之言曰。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车者。不敢指切之也。然则次章桃李之义。亦可以推见。而王姬尚不敢指切。况王姬之颜色乎。女子尚不可以称色。况男子而称色乎。郑氏之论误矣。集传只曰桃李以兴男女。则非取之郑氏也决矣。桃夭之不取古注。意亦仿此。
驺虞
御制条问曰。庶草蕃茂则非独茁葭也。鸟兽咸若则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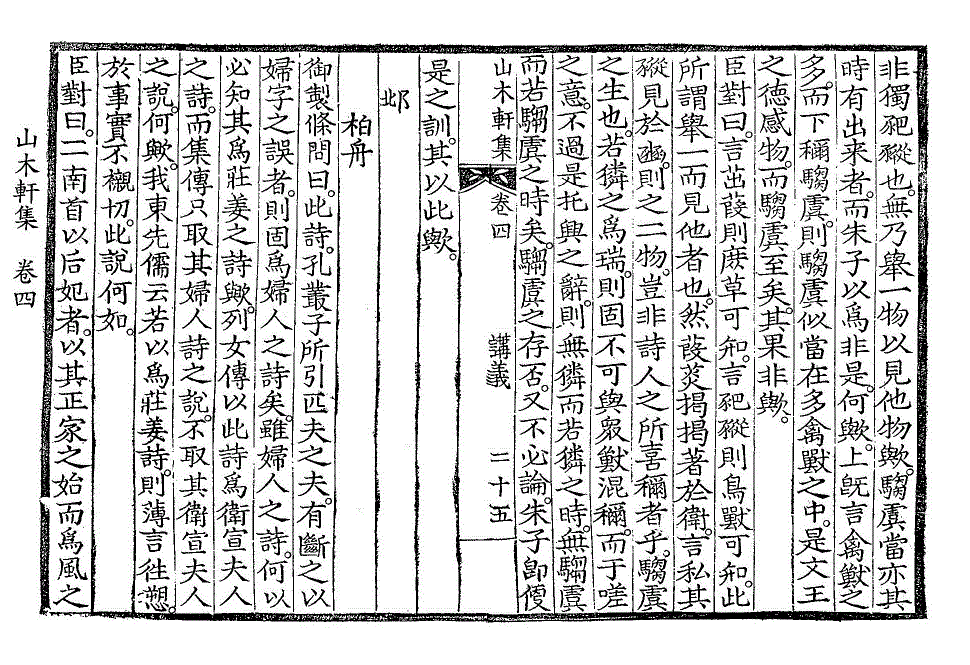 非独豝豵也。无乃举一物以见他物欤。驺虞当亦其时有出来者。而朱子以为非是。何欤。上既言禽兽之多。而下称驺虞。则驺虞似当在多禽兽之中。是文王之德感物。而驺虞至矣。其果非欤。
非独豝豵也。无乃举一物以见他物欤。驺虞当亦其时有出来者。而朱子以为非是。何欤。上既言禽兽之多。而下称驺虞。则驺虞似当在多禽兽之中。是文王之德感物。而驺虞至矣。其果非欤。臣对曰。言茁葭则庶草可知。言豝豵则鸟兽可知。此所谓举一而见他者也。然葭菼揭揭著于卫。言私其豵见于豳。则之二物。岂非诗人之所喜称者乎。驺虞之生也。若獜之为瑞。则固不可与众兽混称。而于嗟之意。不过是托兴之辞。则无獜而若獜之时。无驺虞而若驺虞之时矣。驺虞之存否。又不必论。朱子即便是之训。其以此欤。
邶
柏舟
御制条问曰。此诗。孔丛子所引匹夫之夫。有断之以妇字之误者。则固为妇人之诗矣。虽妇人之诗。何以必知其为庄姜之诗欤。列女传以此诗为卫宣夫人之诗。而集传只取其妇人诗之说。不取其卫宣夫人之说。何欤。我东先儒云若以为庄姜诗。则薄言往愬。于事实不衬切。此说何如。
臣对曰。二南首以后妃者。以其正家之始而为风之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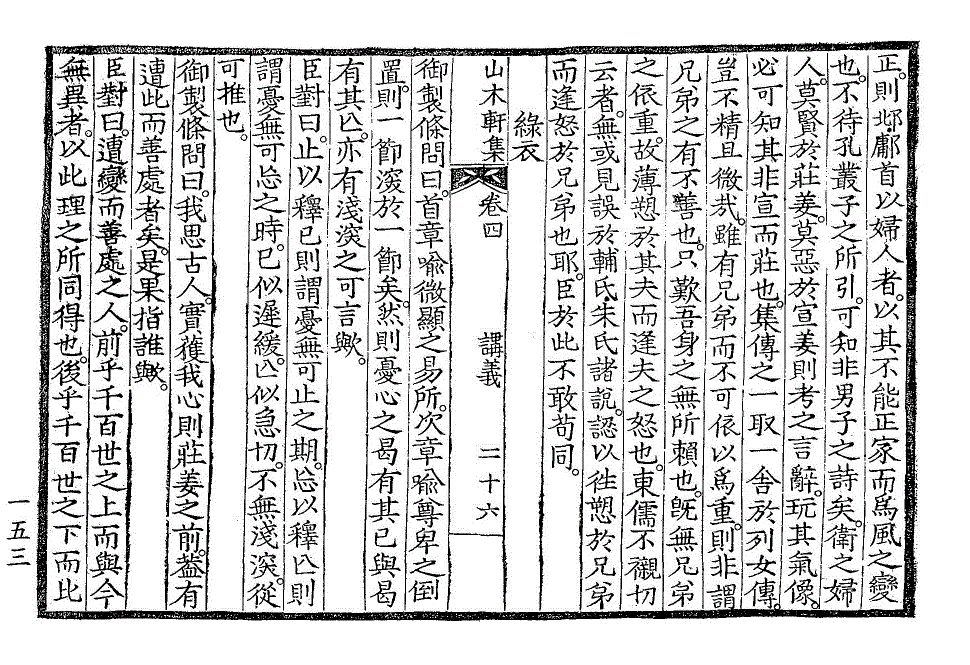 正。则邶,鄘首以妇人者。以其不能正家而为风之变也。不待孔丛子之所引。可知非男子之诗矣。卫之妇人。莫贤于庄姜。莫恶于宣姜则考之言辞。玩其气像。必可知其非宣而庄也。集传之一取一舍于列女传。岂不精且微哉。虽有兄弟而不可依以为重。则非谓兄弟之有不善也。只叹吾身之无所赖也。既无兄弟之依重。故薄愬于其夫而逢夫之怒也。东儒不衬切云者。无或见误于辅氏,朱氏诸说。认以往愬于兄弟而逢怒于兄弟也耶。臣于此不敢苟同。
正。则邶,鄘首以妇人者。以其不能正家而为风之变也。不待孔丛子之所引。可知非男子之诗矣。卫之妇人。莫贤于庄姜。莫恶于宣姜则考之言辞。玩其气像。必可知其非宣而庄也。集传之一取一舍于列女传。岂不精且微哉。虽有兄弟而不可依以为重。则非谓兄弟之有不善也。只叹吾身之无所赖也。既无兄弟之依重。故薄愬于其夫而逢夫之怒也。东儒不衬切云者。无或见误于辅氏,朱氏诸说。认以往愬于兄弟而逢怒于兄弟也耶。臣于此不敢苟同。绿衣
御制条问曰。首章喻微显之易所。次章喻尊卑之倒置。则一节深于一节矣。然则忧心之曷有其已与曷有其亡。亦有浅深之可言欤。
臣对曰。止以释已则谓忧无可止之期。忘以释亡则谓忧无可忘之时。已似迟缓。亡似急切。不无浅深。从可推也。
御制条问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则庄姜之前。盖有遭此而善处者矣。是果指谁欤。
臣对曰。遭变而善处之人。前乎千百世之上而与今无异者。以此理之所同得也。后乎千百世之下而比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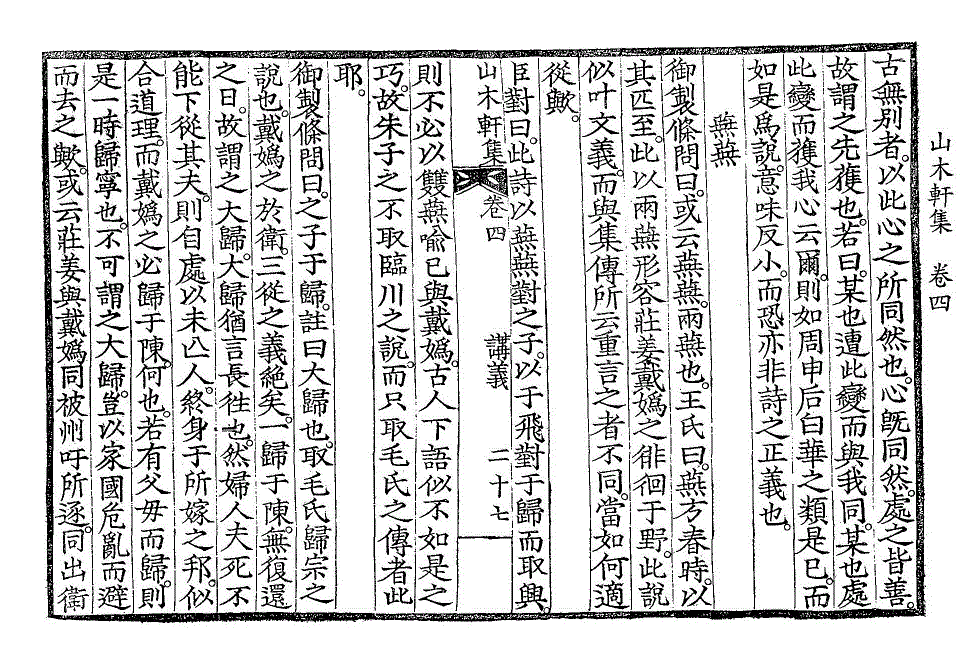 古无别者。以此心之所同然也。心既同然。处之皆善。故谓之先获也。若曰。某也遭此变而与我同。某也处此变而获我心云尔。则如周申后白华之类是已。而如是为说。意味反小。而恐亦非诗之正义也。
古无别者。以此心之所同然也。心既同然。处之皆善。故谓之先获也。若曰。某也遭此变而与我同。某也处此变而获我心云尔。则如周申后白华之类是已。而如是为说。意味反小。而恐亦非诗之正义也。燕燕
御制条问曰。或云燕燕。两燕也。王氏曰。燕方春时。以其匹至。此以两燕形容庄姜,戴妫之徘徊于野。此说似叶文义。而与集传所云重言之者不同。当如何适从欤。
臣对曰。此诗以燕燕对之子。以于飞对于归而取兴。则不必以双燕喻己与戴妫。古人下语似不如是之巧。故朱子之不取临川之说。而只取毛氏之传者此耶。
御制条问曰。之子于归。注曰大归也。取毛氏归宗之说也。戴妫之于卫。三从之义绝矣。一归于陈。无复还之日。故谓之大归。大归犹言长往也。然妇人夫死不能下从其夫。则自处以未亡人。终身于所嫁之邦。似合道理。而戴妫之必归于陈。何也。若有父母而归。则是一时归宁也。不可谓之大归。岂以家国危乱而避而去之欤。或云庄姜与戴妫同被州吁所逐。同出卫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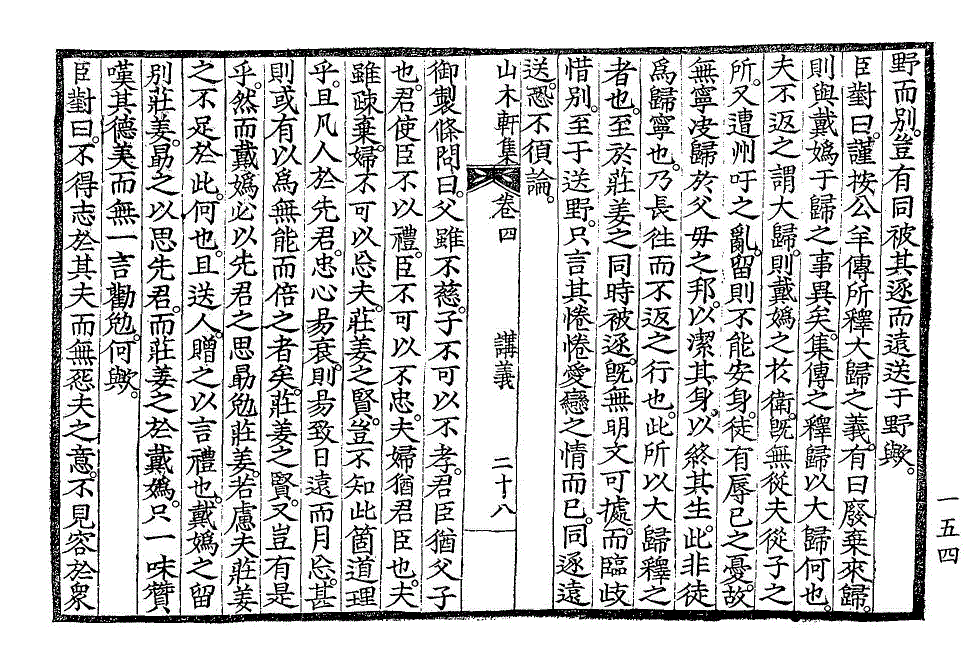 野而别。岂有同被其逐而远送于野欤。
野而别。岂有同被其逐而远送于野欤。臣对曰。谨按公羊传所释大归之义。有曰废弃来归。则与戴妫于归之事异矣。集传之释归以大归何也。夫不返之谓大归。则戴妫之于卫。既无从夫从子之所。又遭州吁之乱。留则不能安身。徒有辱己之忧。故无宁决归于父母之邦。以洁其身。以终其生。此非徒为归宁也。乃长往而不返之行也。此所以大归释之者也。至于庄姜之同时被逐。既无明文可据。而临歧惜别。至于送野。只言其惓惓爱恋之情而已。同逐远送。恐不须论。
御制条问曰。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臣犹父子也。君使臣不以礼。臣不可以不忠。夫妇犹君臣也。夫虽疏弃。妇不可以忘夫。庄姜之贤。岂不知此个道理乎。且凡人于先君。忠心易衰。则易致日远而月忘。甚则或有以为无能而倍之者矣。庄姜之贤。又岂有是乎。然而戴妫必以先君之思勖勉庄姜。若虑夫庄姜之不足于此。何也。且送人。赠之以言礼也。戴妫之留别庄姜。勖之以思先君。而庄姜之于戴妫。只一味赞叹其德美而无一言劝勉。何欤。
臣对曰。不得志于其夫而无怨夫之意。不见容于众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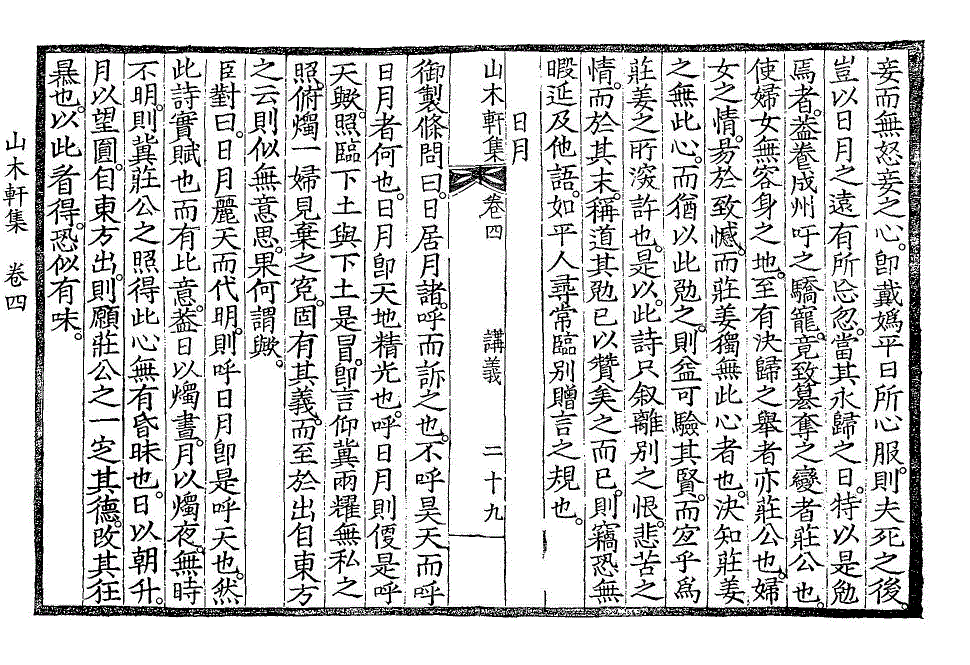 妾而无怒妾之心。即戴妫平日所心服。则夫死之后。岂以日月之远有所忘忽。当其永归之日。特以是勉焉者。盖养成州吁之骄宠。竟致篡夺之变者庄公也。使妇女无容身之地。至有决归之举者亦庄公也。妇女之情。易于致憾。而庄姜独无此心者也。决知庄姜之无此心。而犹以此勉之。则益可验其贤。而宜乎为庄姜之所深许也。是以。此诗只叙离别之恨。悲苦之情。而于其末。称道其勉己以赞美之而已。则窃恐无暇延及他语。如平人寻常临别赠言之规也。
妾而无怒妾之心。即戴妫平日所心服。则夫死之后。岂以日月之远有所忘忽。当其永归之日。特以是勉焉者。盖养成州吁之骄宠。竟致篡夺之变者庄公也。使妇女无容身之地。至有决归之举者亦庄公也。妇女之情。易于致憾。而庄姜独无此心者也。决知庄姜之无此心。而犹以此勉之。则益可验其贤。而宜乎为庄姜之所深许也。是以。此诗只叙离别之恨。悲苦之情。而于其末。称道其勉己以赞美之而已。则窃恐无暇延及他语。如平人寻常临别赠言之规也。日月
御制条问曰。日居月诸。呼而诉之也。不呼昊天而呼日月者何也。日月即天地精光也。呼日月则便是呼天欤。照临下土与下土是冒。即言仰冀两耀无私之照。俯烛一妇见弃之冤。固有其义。而至于出自东方之云则似无意思。果何谓欤。
臣对曰。日月丽天而代明。则呼日月即是呼天也。然此诗实赋也而有比意。盖日以烛昼。月以烛夜。无时不明。则冀庄公之照得此心无有昏昧也。日以朝升。月以望圆。自东方出。则愿庄公之一定其德。改其狂暴也。以此看得。恐似有味。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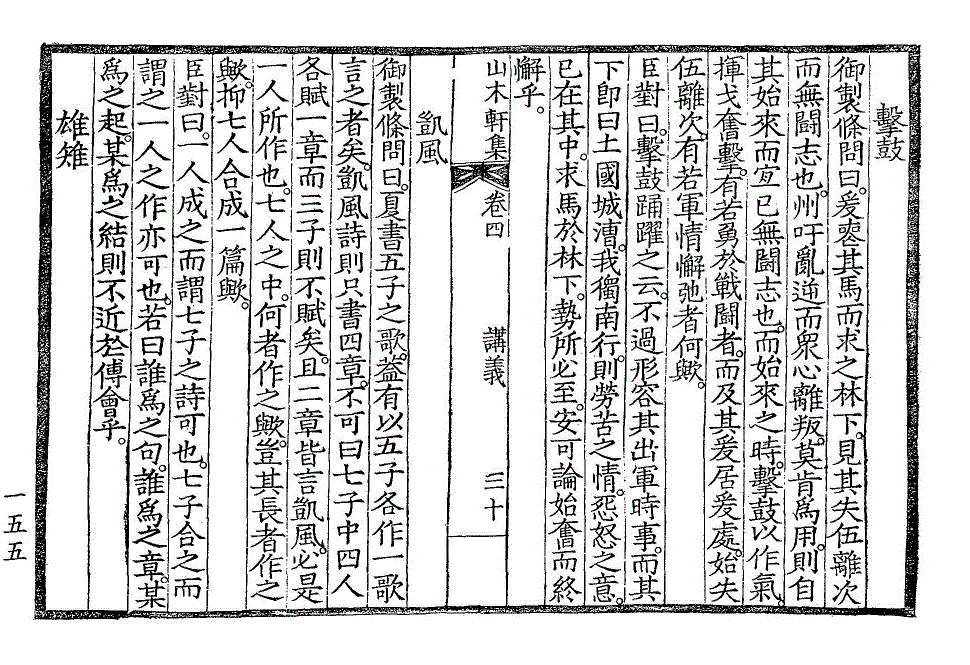 击鼓
击鼓御制条问曰。爰丧其马而求之林下。见其失伍离次而无斗志也。州吁乱逆而众心离叛。莫肯为用。则自其始来而宜已无斗志也。而始来之时。击鼓以作气。挥戈奋击。有若勇于战斗者。而及其爰居爰处。始失伍离次。有若军情懈弛者何欤。
臣对曰。击鼓踊跃之云。不过形容其出军时事。而其下即曰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则劳苦之情。怨怒之意。已在其中。求马于林下。势所必至。安可论始奋而终懈乎。
凯风
御制条问曰。夏书五子之歌。盖有以五子各作一歌言之者矣。凯风诗则只书四章。不可曰七子中四人各赋一章而三子则不赋矣。且二章皆言凯风。必是一人所作也。七人之中。何者作之欤。岂其长者作之欤。抑七人合成一篇欤。
臣对曰。一人成之而谓七子之诗可也。七子合之而谓之一人之作亦可也。若曰谁为之句。谁为之章。某为之起。某为之结则不近于傅会乎。
雄雉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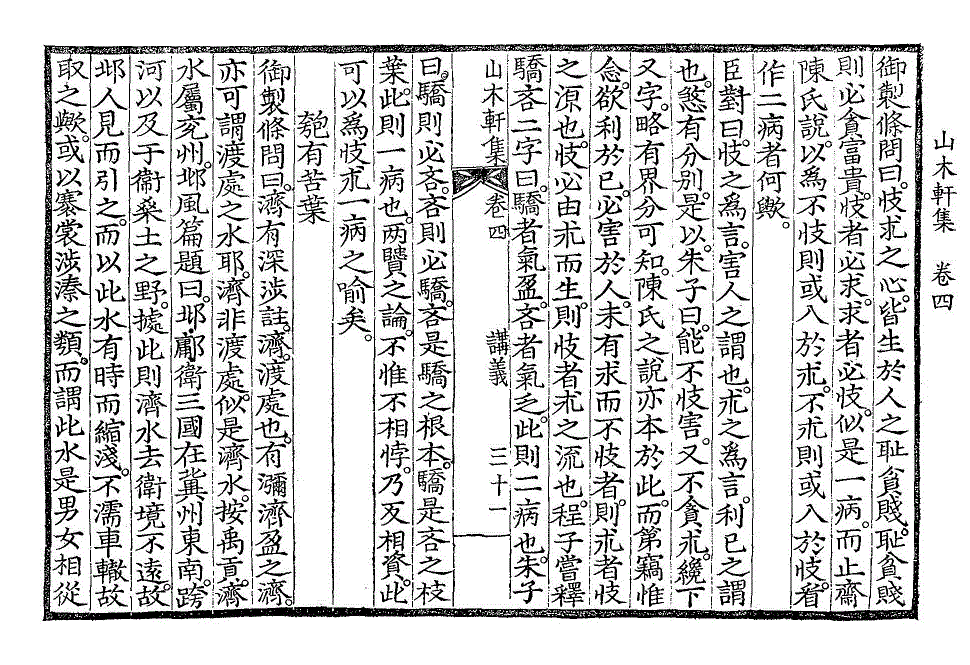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忮求之心。皆生于人之耻贫贱。耻贫贱则必贪富贵。忮者必求。求者必忮。似是一病。而止斋陈氏说。以为不忮则或入于求。不求则或入于忮。看作二病者何欤。
御制条问曰。忮求之心。皆生于人之耻贫贱。耻贫贱则必贪富贵。忮者必求。求者必忮。似是一病。而止斋陈氏说。以为不忮则或入于求。不求则或入于忮。看作二病者何欤。臣对曰。忮之为言。害人之谓也。求之为言。利己之谓也。煞有分别。是以。朱子曰。能不忮害。又不贪求。才下又字。略有界分可知。陈氏之说亦本于此。而第窃惟念。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未有求而不忮者。则求者忮之源也。忮必由求而生。则忮者求之流也。程子尝释骄吝二字曰。骄者气盈。吝者气乏。此则二病也。朱子曰。骄则必吝。吝则必骄。吝是骄之根本。骄是吝之枝叶。此则一病也。两贤之论。不惟不相悖。乃反相资。此可以为忮求一病之喻矣。
匏有苦叶
御制条问曰。济有深涉注。济。渡处也。有㳽济盈之济。亦可谓渡处之水耶。济非渡处。似是济水。按禹贡。济水属兖州。邶风篇题曰。邶,鄘,卫三国在冀州东南。跨河以及于卫桑土之野。据此则济水去卫境不远。故邶人见而引之。而以此水有时而缩浅。不濡车辙故取之欤。或以褰裳涉溱之类。而谓此水是男女相从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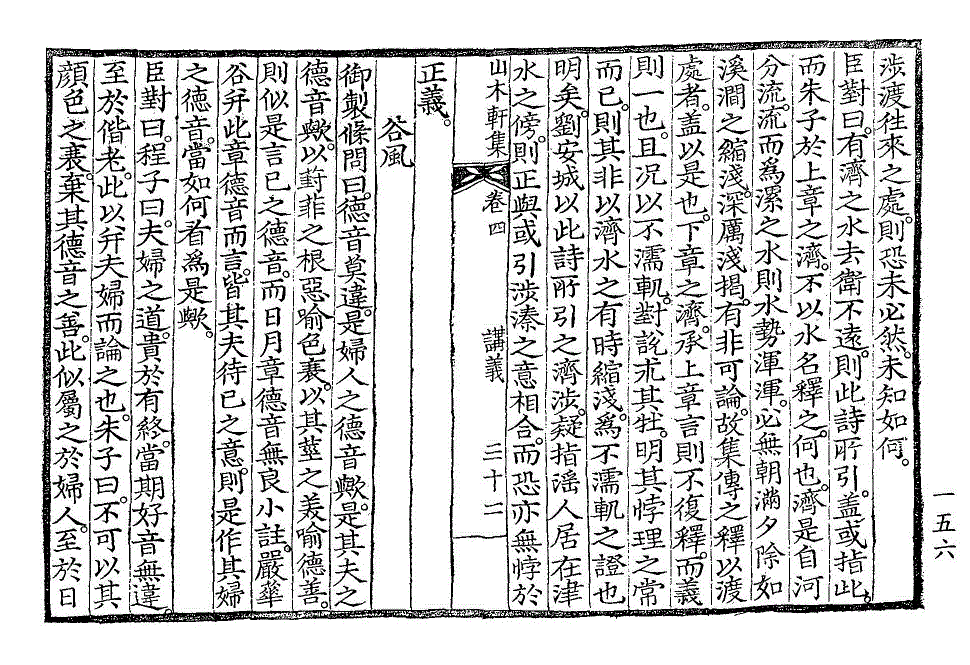 涉渡往来之处。则恐未必然。未知如何。
涉渡往来之处。则恐未必然。未知如何。臣对曰。有济之水去卫不远。则此诗所引。盖或指此。而朱子于上章之济。不以水名释之。何也。济是自河分流。流而为漯之水则水势浑浑。必无朝满夕除如溪涧之缩浅。深厉浅揭。有非可论。故集传之释以渡处者。盖以是也。下章之济。承上章言则不复释。而义则一也。且况以不濡轨。对说求其牡。明其悖理之常而已。则其非以济水之有时缩浅。为不濡轨之證也明矣。刘安城以此诗所引之济涉。疑指淫人居在津水之傍。则正与或引涉溱之意相合。而恐亦无悖于正义。
谷风
御制条问曰。德音莫违。是妇人之德音欤。是其夫之德音欤。以葑菲之根恶喻色衰。以其茎之美喻德善。则似是言己之德音。而日月章德音无良小注。严华谷并此章德音而言。皆其夫待已之意。则是作其妇之德音。当如何看为是欤。
臣对曰。程子曰。夫妇之道。贵于有终。当期好音无违。至于偕老。此以并夫妇而论之也。朱子曰。不可以其颜色之衰。弃其德音之善。此似属之于妇人。至于日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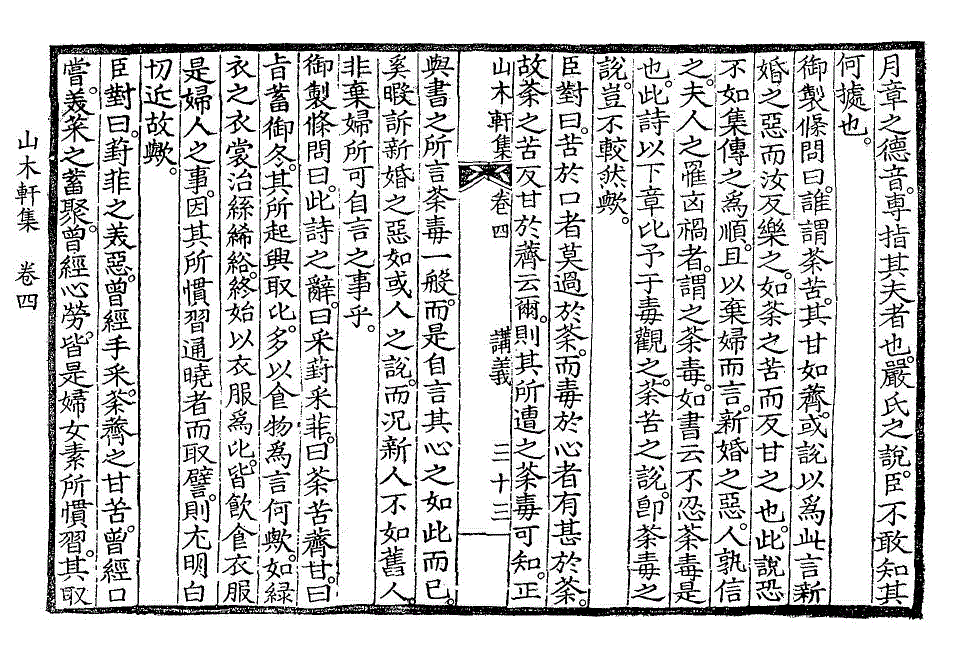 月章之德音。专指其夫者也。严氏之说。臣不敢知其何据也。
月章之德音。专指其夫者也。严氏之说。臣不敢知其何据也。御制条问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或说以为此言新婚之恶而汝反乐之。如荼之苦而反甘之也。此说恐不如集传之为顺。且以弃妇而言。新婚之恶。人孰信之。夫人之罹凶祸者。谓之荼毒。如书云不忍荼毒是也。此诗以下章比予于毒观之。荼苦之说。即荼毒之说。岂不较然欤。
臣对曰。苦于口者莫过于荼。而毒于心者有甚于荼。故荼之苦反甘于荠云尔。则其所遭之荼毒可知。正与书之所言荼毒一般。而是自言其心之如此而已。奚暇诉新婚之恶如或人之说。而况新人不如旧人。非弃妇所可自言之事乎。
御制条问曰。此诗之辞。曰采葑采菲。曰荼苦荠甘。曰旨蓄御冬。其所起兴取比。多以食物为言何欤。如绿衣之衣裳治丝絺绤。终始以衣服为比。皆饮食衣服是妇人之事。因其所惯习通晓者而取譬。则尤明白切近故欤。
臣对曰。葑菲之美恶。曾经手采。荼荠之甘苦。曾经口尝。美菜之蓄聚。曾经心劳。皆是妇女素所惯习。其取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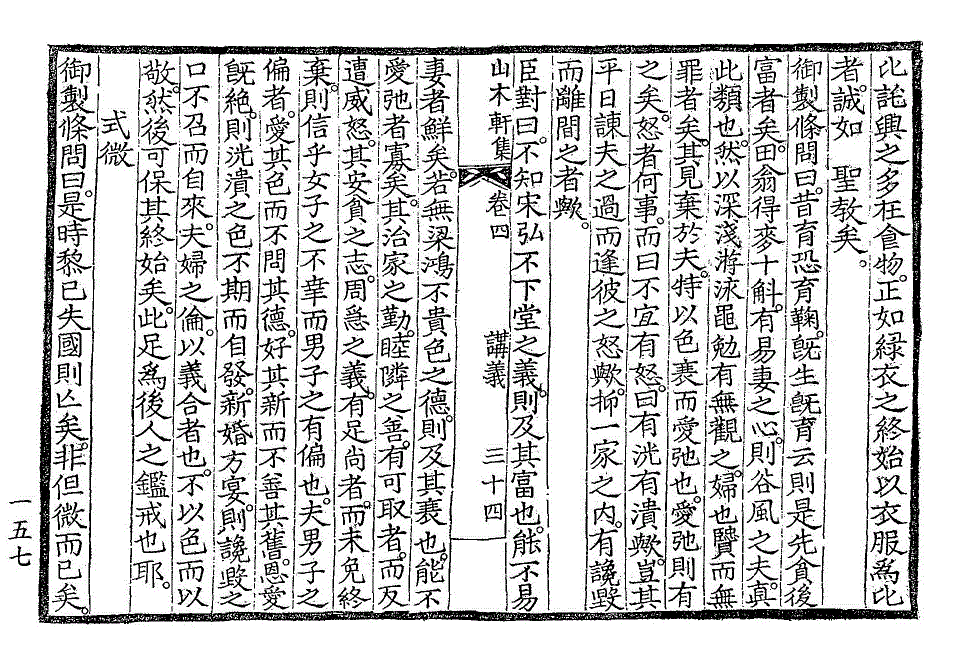 比托兴之多在食物。正如绿衣之终始以衣服为比者。诚如 圣教矣。
比托兴之多在食物。正如绿衣之终始以衣服为比者。诚如 圣教矣。御制条问曰。昔育恐育鞠。既生既育云则是先贫后富者矣。田翁得麦十斛。有易妻之心。则谷风之夫。真此类也。然以深浅游泳黾勉有无观之。妇也贤而无罪者矣。其见弃于夫。特以色衰而爱弛也。爱弛则有之矣。怒者何事。而曰不宜有怒。曰有洸有溃欤。岂其平日谏夫之过而逢彼之怒欤。抑一家之内。有谗毁而离间之者欤。
臣对曰。不知宋弘不下堂之义。则及其富也。能不易妻者鲜矣。若无梁鸿不贵色之德。则及其衰也。能不爱弛者寡矣。其治家之勤。睦邻之善。有可取者。而反遭威怒。其安贫之志。周急之义。有足尚者。而未免终弃。则信乎女子之不幸而男子之有偏也。夫男子之偏者。爱其色而不问其德。好其新而不善其旧。恩爱既绝。则洸溃之色不期而自发。新婚方宴。则谗毁之口不召而自来。夫妇之伦。以义合者也。不以色而以敬。然后可保其终始矣。此足为后人之鉴戒也耶。
式微
御制条问曰。是时黎已失国则亡矣。非但微而已矣。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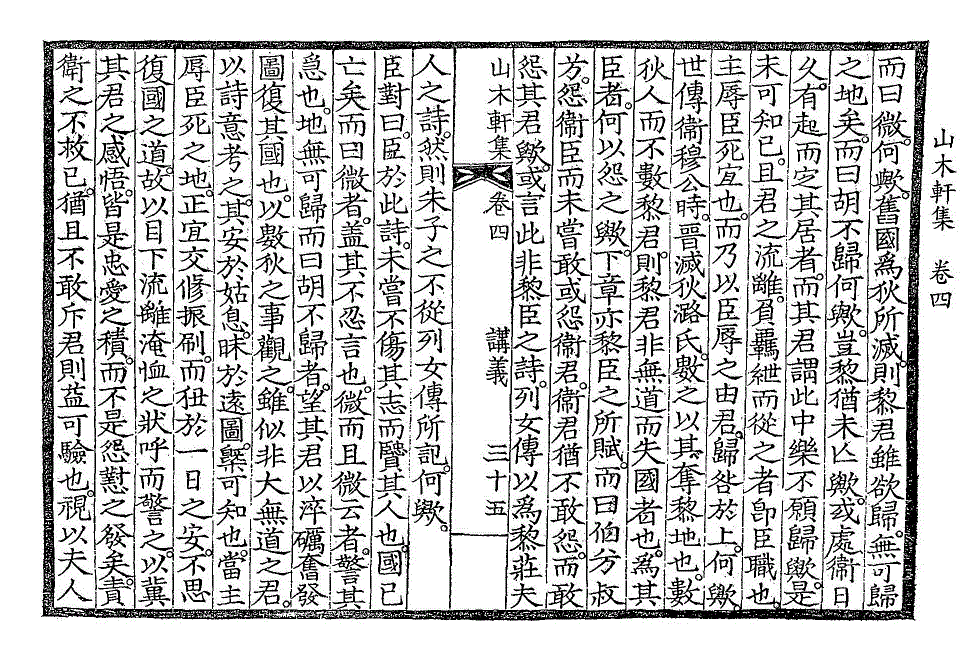 而曰微。何欤。旧国为狄所灭。则黎君虽欲归。无可归之地矣。而曰胡不归何欤。岂黎犹未亡欤。或处卫日久。有起而定其居者。而其君谓此中乐不愿归欤。是未可知已。且君之流离。负羁绁而从之者即臣职也。主辱臣死宜也。而乃以臣辱之由君。归咎于上。何欤。世传卫穆公时。晋灭狄潞氏。数之以其夺黎地也。数狄人而不数黎君。则黎君非无道而失国者也。为其臣者。何以怨之欤。下章亦黎臣之所赋。而曰伯兮叔兮。怨卫臣而未尝敢或怨卫君。卫君犹不敢怨。而敢怨其君欤。或言此非黎臣之诗。列女传以为黎庄夫人之诗。然则朱子之不从列女传所记。何欤。
而曰微。何欤。旧国为狄所灭。则黎君虽欲归。无可归之地矣。而曰胡不归何欤。岂黎犹未亡欤。或处卫日久。有起而定其居者。而其君谓此中乐不愿归欤。是未可知已。且君之流离。负羁绁而从之者即臣职也。主辱臣死宜也。而乃以臣辱之由君。归咎于上。何欤。世传卫穆公时。晋灭狄潞氏。数之以其夺黎地也。数狄人而不数黎君。则黎君非无道而失国者也。为其臣者。何以怨之欤。下章亦黎臣之所赋。而曰伯兮叔兮。怨卫臣而未尝敢或怨卫君。卫君犹不敢怨。而敢怨其君欤。或言此非黎臣之诗。列女传以为黎庄夫人之诗。然则朱子之不从列女传所记。何欤。臣对曰。臣于此诗。未尝不伤其志而贤其人也。国已亡矣而曰微者。盖其不忍言也。微而且微云者。警其急也。地无可归而曰胡不归者。望其君以淬砺奋发图复其国也。以数狄之事观之。虽似非大无道之君。以诗意考之。其安于姑息。昧于远图。槩可知也。当主辱臣死之地。正宜交修振刷。而狃于一日之安。不思复国之道。故以目下流离淹恤之状呼而警之。以冀其君之感悟。皆是忠爱之积。而不是怨怼之发矣。责卫之不救己。犹且不敢斥君则益可验也。视以夫人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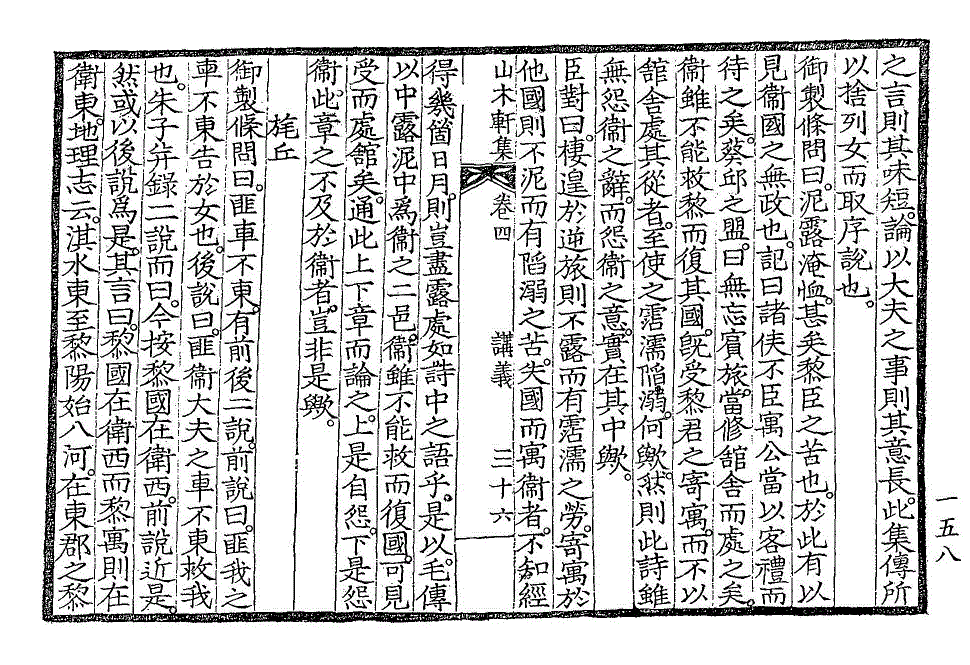 之言则其味短。论以大夫之事则其意长。此集传所以舍列女而取序说也。
之言则其味短。论以大夫之事则其意长。此集传所以舍列女而取序说也。御制条问曰。泥露淹恤。甚矣黎臣之苦也。于此有以见卫国之无政也。记曰诸侯不臣寓公当以客礼而待之矣。葵邱之盟。曰无忘宾旅。当修馆舍而处之矣。卫虽不能救黎而复其国。既受黎君之寄寓。而不以馆舍处其从者。至使之沾濡陷溺。何欤。然则此诗虽无怨卫之辞。而怨卫之意。实在其中欤。
臣对曰。栖遑于逆旅则不露而有沾濡之劳。寄寓于他国则不泥而有陷溺之苦。失国而寓卫者。不知经得几个日月。则岂尽露处如诗中之语乎。是以。毛传以中露泥中为卫之二邑。卫虽不能救而复国。可见受而处馆矣。通此上下章而论之。上是自怨。下是怨卫。此章之不及于卫者。岂非是欤。
旄丘
御制条问曰。匪车不东。有前后二说。前说曰。匪我之车不东告于女也。后说曰。匪卫大夫之车不东救我也。朱子并录二说而曰。今按黎国在卫西。前说近是。然或以后说为是。其言曰。黎国在卫西而黎寓则在卫东。地理志云。淇水东至黎阳始八河。在东郡之黎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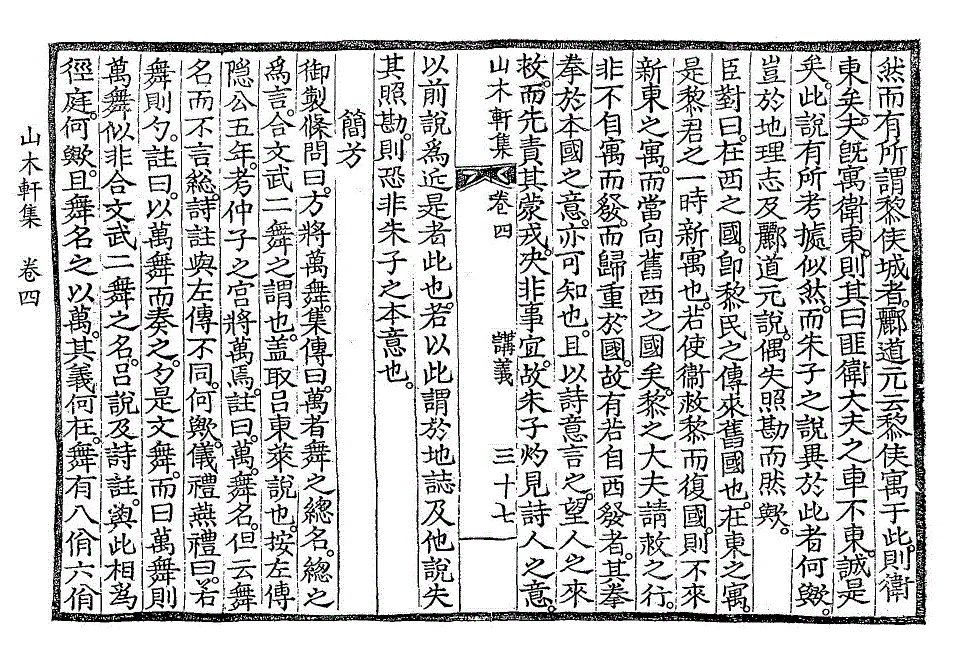 然而有所谓黎侯城者。郦道元云黎侯寓于此则卫东矣。夫既寓卫东。则其曰匪卫大夫之车不东。诚是矣。此说有所考据似然。而朱子之说异于此者何欤。岂于地理志及郦道元说。偶失照勘而然欤。
然而有所谓黎侯城者。郦道元云黎侯寓于此则卫东矣。夫既寓卫东。则其曰匪卫大夫之车不东。诚是矣。此说有所考据似然。而朱子之说异于此者何欤。岂于地理志及郦道元说。偶失照勘而然欤。臣对曰。在西之国。即黎民之传来旧国也。在东之寓。是黎君之一时新寓也。若使卫救黎而复国。则不来新东之寓。而当向旧西之国矣。黎之大夫请救之行。非不自寓而发。而归重于国。故有若自西发者。其拳拳于本国之意。亦可知也。且以诗意言之。望人之来救。而先责其蒙戎。决非事宜。故朱子灼见诗人之意。以前说为近是者此也。若以此谓于地志及他说失其照勘。则恐非朱子之本意也。
简兮
御制条问曰。方将万舞。集传曰。万者舞之总名。总之为言。合文武二舞之谓也。盖取吕东莱说也。按左传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将万焉。注曰。万。舞名。但云舞名而不言总。诗注与左传不同。何欤。仪礼燕礼曰。若舞则勺。注曰。以万舞而奏之。勺是文舞。而曰万舞则万舞似非合文武二舞之名。吕说及诗注。与此相为径庭。何欤。且舞名之以万。其义何在。舞有八佾六佾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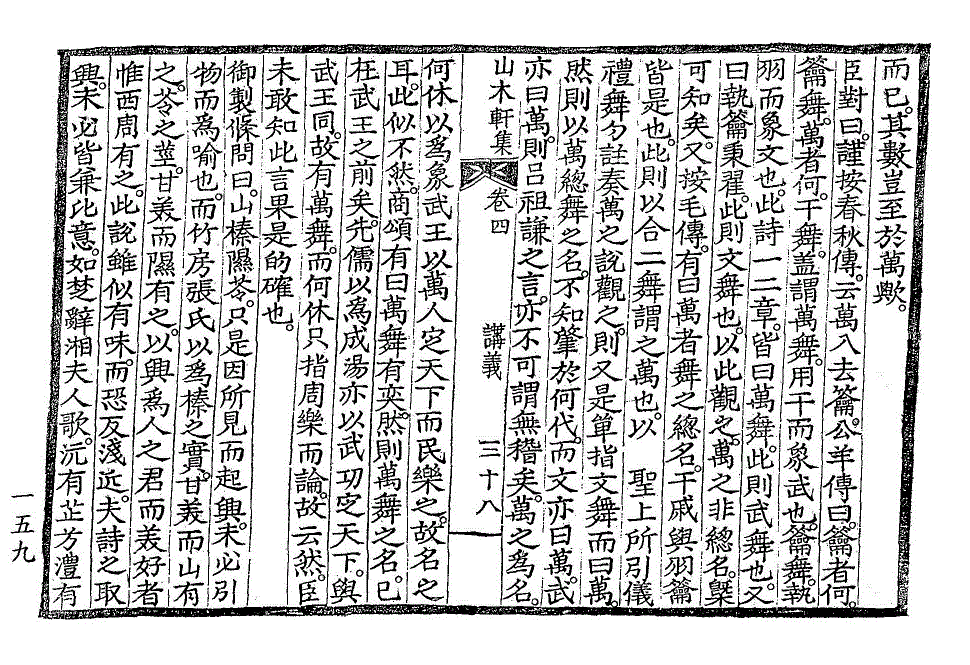 而已。其数岂至于万欤。
而已。其数岂至于万欤。臣对曰。谨按春秋传。云万入去籥。公羊传曰。籥者何。籥舞。万者何。干舞。盖谓万舞。用干而象武也。籥舞。执羽而象文也。此诗一二章。皆曰万舞。此则武舞也。又曰执籥秉翟。此则文舞也。以此观之。万之非总名。槩可知矣。又按毛传。有曰万者舞之总名。干戚与羽籥皆是也。此则以合二舞谓之万也。以 圣上所引仪礼舞勺注奏万之说观之。则又是单指文舞而曰万。然则以万总舞之名。不知肇于何代。而文亦曰万。武亦曰万。则吕祖谦之言。亦不可谓无稽矣。万之为名。何休以为象武王以万人定天下而民乐之。故名之耳。此似不然。商颂有曰万舞有奕。然则万舞之名。已在武王之前矣。先儒以为成汤亦以武功定天下。与武王同。故有万舞。而何休只指周乐而论。故云然。臣未敢知此言果是的确也。
御制条问曰。山榛隰苓。只是因所见而起兴。未必引物而为喻也。而竹房张氏以为榛之实。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茎。甘美而隰有之。以兴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此说虽似有味。而恐反浅近。夫诗之取兴。未必皆兼比意。如楚辞湘夫人歌。沅有芷兮澧有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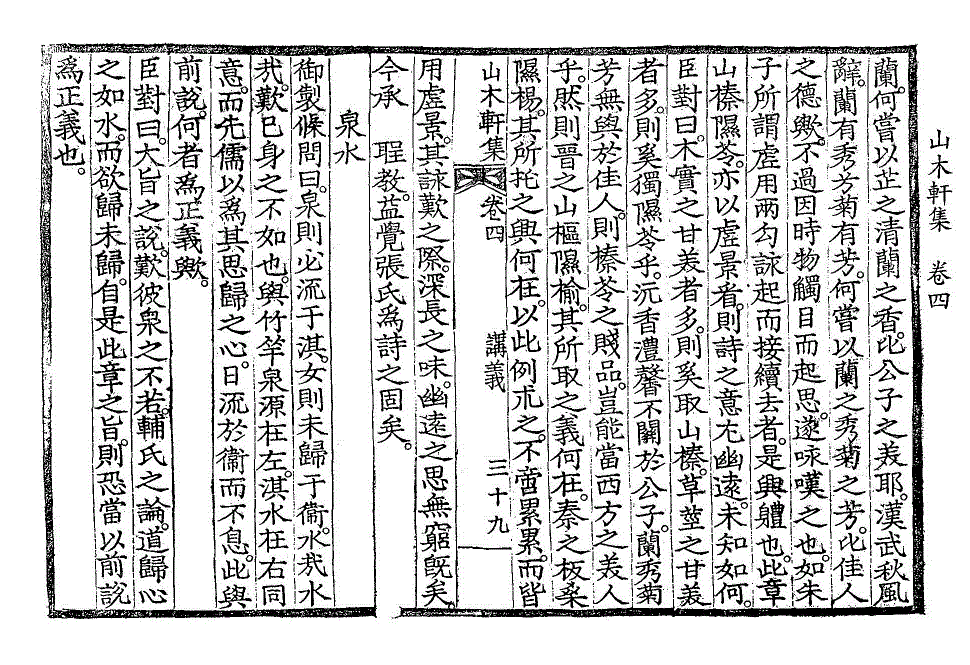 兰。何尝以芷之清兰之香。比公子之美耶。汉武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何尝以兰之秀菊之芳。比佳人之德欤。不过因时物触目而起思。遂咏叹之也。如朱子所谓虚用两勾咏起而接续去者。是兴体也。此章山榛隰苓。亦以虚景看。则诗之意尤幽远。未知如何。
兰。何尝以芷之清兰之香。比公子之美耶。汉武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何尝以兰之秀菊之芳。比佳人之德欤。不过因时物触目而起思。遂咏叹之也。如朱子所谓虚用两勾咏起而接续去者。是兴体也。此章山榛隰苓。亦以虚景看。则诗之意尤幽远。未知如何。臣对曰。木实之甘美者多。则奚取山榛。草茎之甘美者多。则奚独隰苓乎。沅香澧馨不关于公子。兰秀菊芳无与于佳人。则榛苓之贱品。岂能当西方之美人乎。然则晋之山枢隰榆。其所取之义何在。秦之板桑隰杨。其所托之兴何在。以此例求之。不啻累累。而皆用虚景。其咏叹之际。深长之味。幽远之思无穷既矣。今承 圣教。益觉张氏为诗之固矣。
泉水
御制条问曰。泉则必流于淇。女则未归于卫。水哉水哉。叹己身之不如也。与竹竿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同意。而先儒以为其思归之心。日流于卫而不息。此与前说。何者为正义欤。
臣对曰。大旨之说。叹彼泉之不若。辅氏之论。道归心之如水。而欲归未归。自是此章之旨。则恐当以前说为正义也。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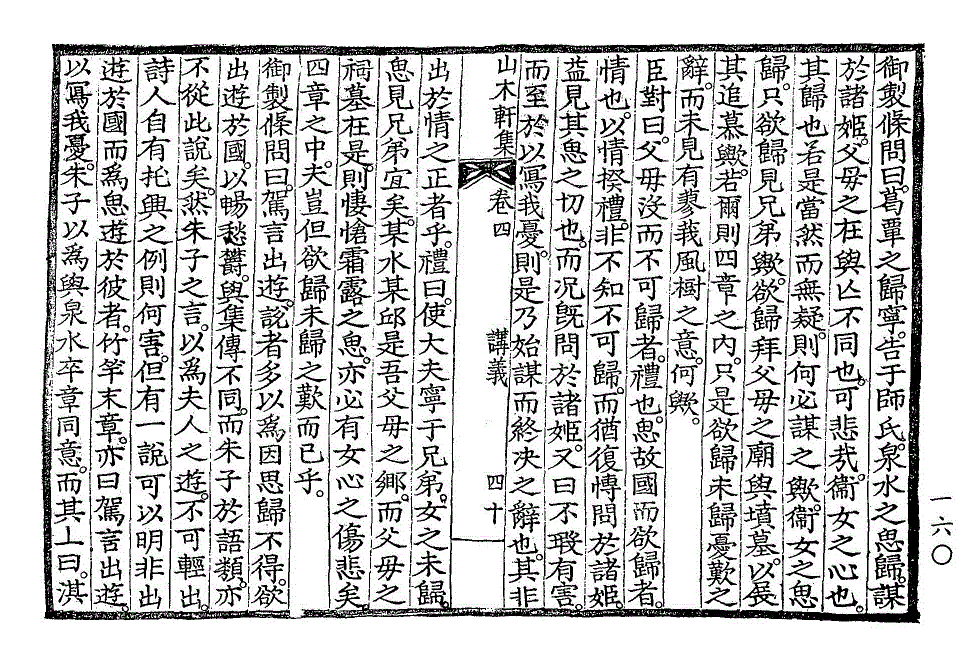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葛覃之归宁。告于师氏。泉水之思归。谋于诸姬。父母之在与亡不同也。可悲哉。卫女之心也。其归也若是当然而无疑。则何必谋之欤。卫女之思归。只欲归见兄弟欤。欲归拜父母之庙与坟墓。以展其追慕欤。若尔则四章之内。只是欲归未归忧叹之辞。而未见有蓼莪风树之意。何欤。
御制条问曰。葛覃之归宁。告于师氏。泉水之思归。谋于诸姬。父母之在与亡不同也。可悲哉。卫女之心也。其归也若是当然而无疑。则何必谋之欤。卫女之思归。只欲归见兄弟欤。欲归拜父母之庙与坟墓。以展其追慕欤。若尔则四章之内。只是欲归未归忧叹之辞。而未见有蓼莪风树之意。何欤。臣对曰。父母没而不可归者。礼也。思故国而欲归者。情也。以情揆礼。非不知不可归。而犹复博问于诸姬。益见其思之切也。而况既问于诸姬。又曰不瑕有害。而至于以写我忧。则是乃始谋而终决之辞也。其非出于情之正者乎。礼曰。使大夫宁于兄弟。女之未归。思见兄弟宜矣。某水某邱是吾父母之乡。而父母之祠墓在是。则悽怆霜露之思。亦必有女心之伤悲矣。四章之中。夫岂但欲归未归之叹而已乎。
御制条问曰。驾言出游。说者多以为因思归不得。欲出游于国。以畅愁郁。与集传不同。而朱子于语类。亦不从此说矣。然朱子之言。以为夫人之游。不可轻出。诗人自有托兴之例则何害。但有一说可以明非出游于国而为思游于彼者。竹竿末章。亦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朱子以为与泉水卒章同意。而其上曰。淇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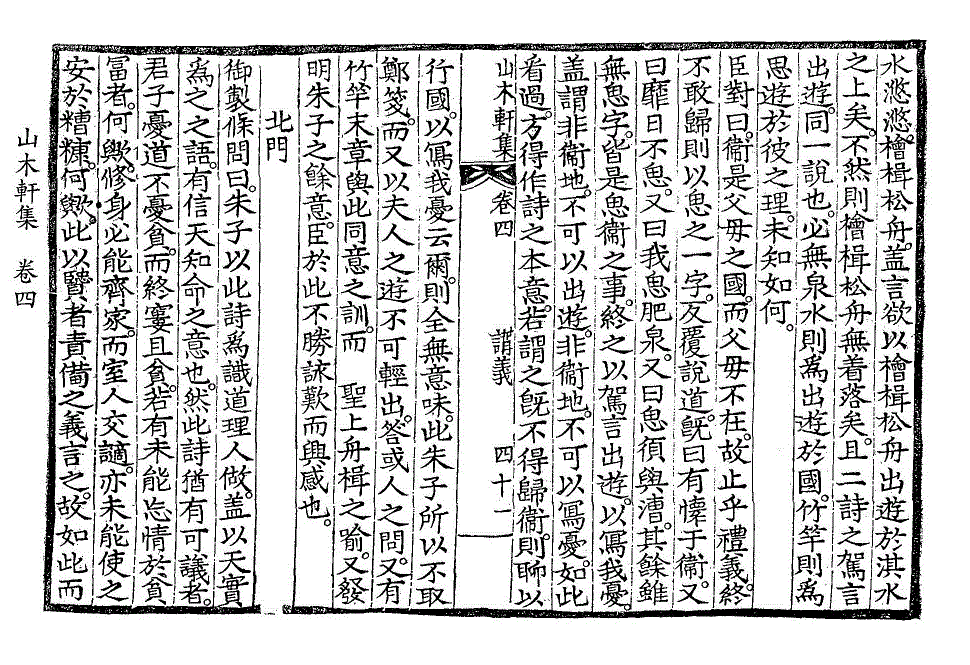 水浟浟。桧楫松舟。盖言欲以桧楫松舟出游于淇水之上矣。不然则桧楫松舟无着落矣。且二诗之驾言出游。同一说也。必无泉水则为出游于国。竹竿则为思游于彼之理。未知如何。
水浟浟。桧楫松舟。盖言欲以桧楫松舟出游于淇水之上矣。不然则桧楫松舟无着落矣。且二诗之驾言出游。同一说也。必无泉水则为出游于国。竹竿则为思游于彼之理。未知如何。臣对曰。卫是父母之国。而父母不在。故止乎礼义。终不敢归则以思之一字。反覆说道。既曰有怀于卫。又曰靡日不思。又曰我思肥泉。又曰思须与漕。其馀虽无思字。皆是思卫之事。终之以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盖谓非卫地。不可以出游。非卫地。不可以写忧。如此看过。方得作诗之本意。若谓之既不得归卫。则聊以行国。以写我忧云尔。则全无意味。此朱子所以不取郑笺。而又以夫人之游不可轻出。答或人之问。又有竹竿末章与此同意之训。而 圣上舟楫之喻。又发明朱子之馀意。臣于此不胜咏叹而兴感也。
北门
御制条问曰。朱子以此诗为识道理人做。盖以天实为之之语。有信天知命之意也。然此诗犹有可议者。君子忧道不忧贫。而终窭且贫。若有未能忘情于贫富者。何欤。修身必能齐家。而室人交谪。亦未能使之安于糟糠。何欤。此以贤者责备之义言之。故如此而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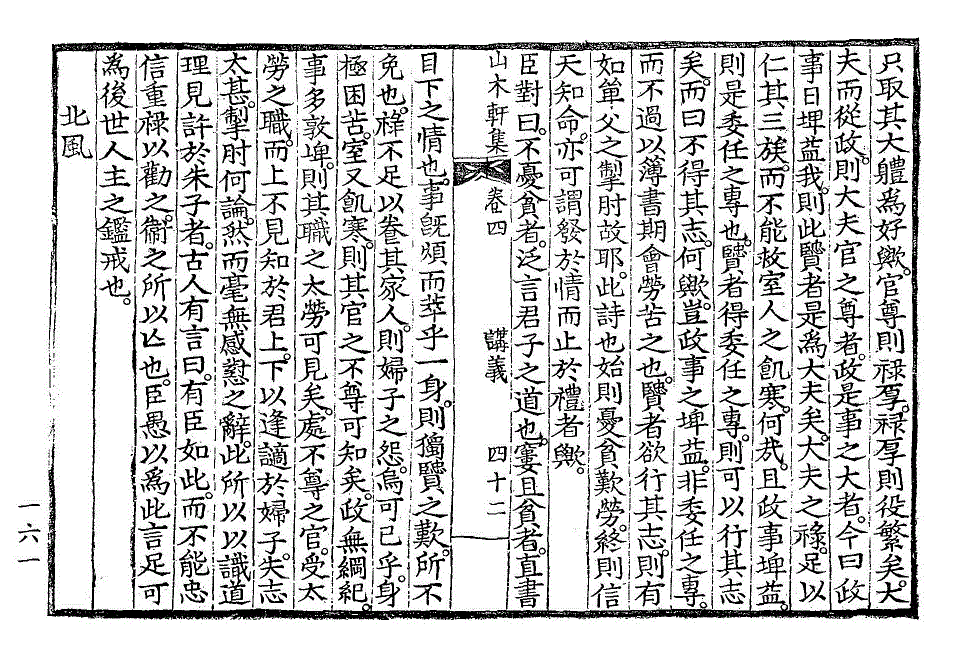 只取其大体为好欤。官尊则禄厚。禄厚则役繁矣。大夫而从政。则大夫官之尊者。政是事之大者。今曰政事日埤益我。则此贤者是为大夫矣。大夫之禄。足以仁其三族。而不能救室人之饥寒。何哉。且政事埤益。则是委任之专也。贤者得委任之专。则可以行其志矣。而曰不得其志。何欤。岂政事之埤益。非委任之专。而不过以簿书期会劳苦之也。贤者欲行其志。则有如单父之掣肘故耶。此诗也始则忧贫叹劳。终则信天知命。亦可谓发于情而止于礼者欤。
只取其大体为好欤。官尊则禄厚。禄厚则役繁矣。大夫而从政。则大夫官之尊者。政是事之大者。今曰政事日埤益我。则此贤者是为大夫矣。大夫之禄。足以仁其三族。而不能救室人之饥寒。何哉。且政事埤益。则是委任之专也。贤者得委任之专。则可以行其志矣。而曰不得其志。何欤。岂政事之埤益。非委任之专。而不过以簿书期会劳苦之也。贤者欲行其志。则有如单父之掣肘故耶。此诗也始则忧贫叹劳。终则信天知命。亦可谓发于情而止于礼者欤。臣对曰。不忧贫者。泛言君子之道也。窭且贫者。直书目下之情也。事既烦而萃乎一身。则独贤之叹。所不免也。禄不足以养其家人。则妇子之怨。乌可已乎。身极困苦。室又饥寒。则其官之不尊可知矣。政无纲纪。事多敦埤。则其职之太劳可见矣。处不尊之官。受太劳之职。而上不见知于君上。下以逢谪于妇子。失志太甚。掣肘何论。然而毫无感怼之辞。此所以以识道理见许于朱子者。古人有言曰。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禄以劝之。卫之所以亡也。臣愚以为此言足可为后世人主之鉴戒也。
北风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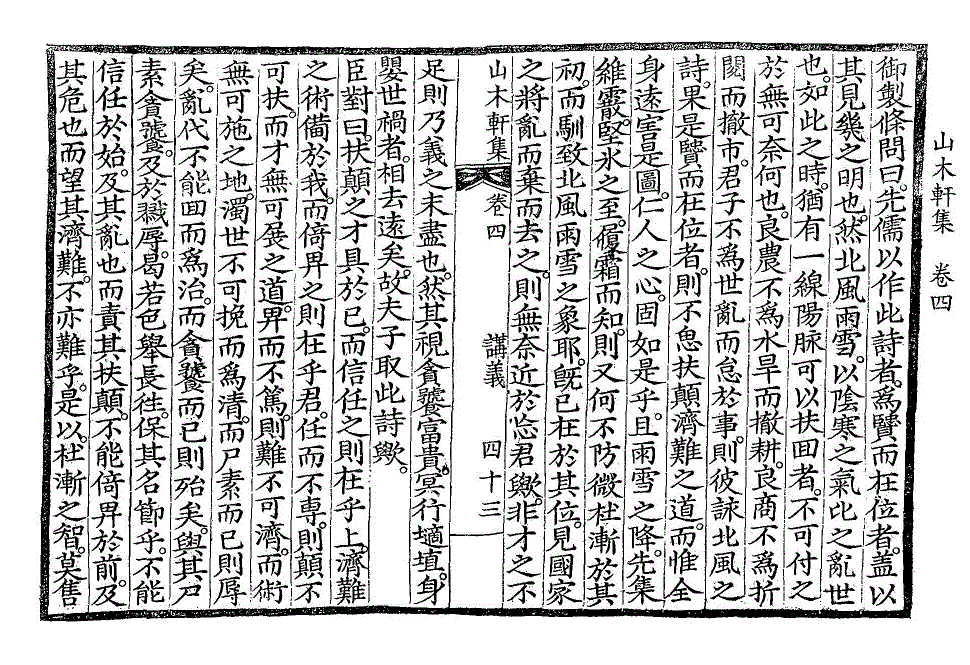 御制条问曰。先儒以作此诗者。为贤而在位者。盖以其见几之明也。然北风雨雪。以阴寒之气比之乱世也。如此之时。犹有一线阳脉可以扶回者。不可付之于无可奈何也。良农不为水旱而撤耕。良商不为折阅而撤市。君子不为世乱而怠于事。则彼咏北风之诗。果是贤而在位者。则不思扶颠济难之道。而惟全身远害是图。仁人之心。固如是乎。且雨雪之降。先集维霰。坚冰之至。履霜而知。则又何不防微杜渐于其初。而驯致北风雨雪之象耶。既已在于其位。见国家之将乱而弃而去之。则无奈近于忘君欤。非才之不足则乃义之未尽也。然其视贪饕富贵。冥行擿埴。身婴世祸者。相去远矣。故夫子取此诗欤。
御制条问曰。先儒以作此诗者。为贤而在位者。盖以其见几之明也。然北风雨雪。以阴寒之气比之乱世也。如此之时。犹有一线阳脉可以扶回者。不可付之于无可奈何也。良农不为水旱而撤耕。良商不为折阅而撤市。君子不为世乱而怠于事。则彼咏北风之诗。果是贤而在位者。则不思扶颠济难之道。而惟全身远害是图。仁人之心。固如是乎。且雨雪之降。先集维霰。坚冰之至。履霜而知。则又何不防微杜渐于其初。而驯致北风雨雪之象耶。既已在于其位。见国家之将乱而弃而去之。则无奈近于忘君欤。非才之不足则乃义之未尽也。然其视贪饕富贵。冥行擿埴。身婴世祸者。相去远矣。故夫子取此诗欤。臣对曰。扶颠之才具于己。而信任之则在乎上。济难之术备于我。而倚畀之则在乎君。任而不专。则颠不可扶。而才无可展之道。畀而不笃。则难不可济。而术无可施之地。浊世不可挽而为清。而尸素而已则辱矣。乱代不能回而为治。而贪饕而已则殆矣。与其尸素贪饕。及于戮辱。曷若色举长往。保其名节乎。不能信任于始。及其乱也而责其扶颠。不能倚畀于前。及其危也而望其济难。不亦难乎。是以。杜渐之智。莫售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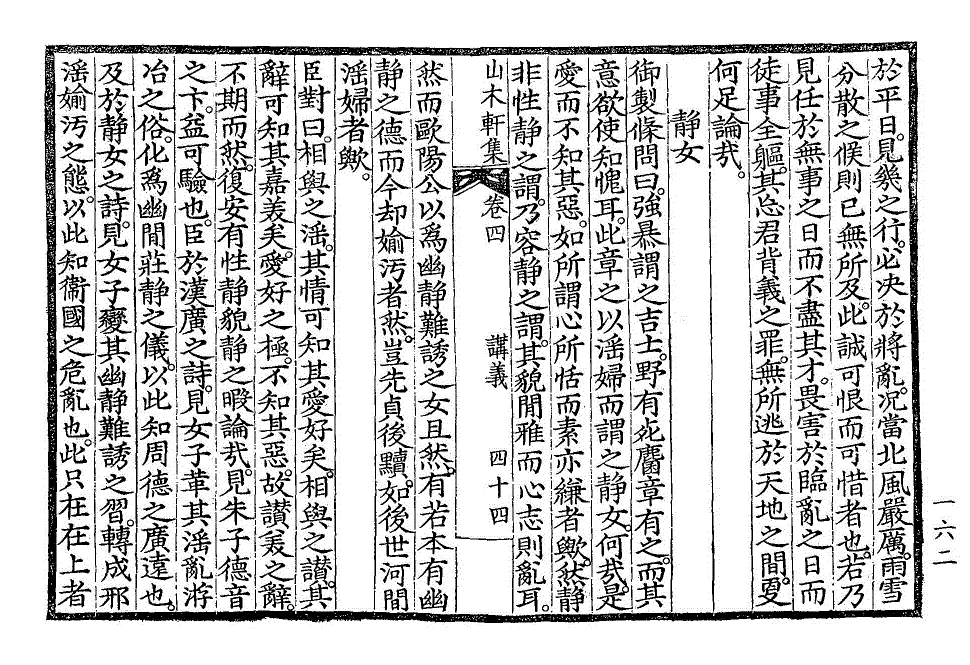 于平日。见几之行。必决于将乱。况当北风严厉。雨雪分散之候则已无所及。此诚可恨而可惜者也。若乃见任于无事之日而不尽其才。畏害于临乱之日而徒事全躯。其忘君背义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更何足论哉。
于平日。见几之行。必决于将乱。况当北风严厉。雨雪分散之候则已无所及。此诚可恨而可惜者也。若乃见任于无事之日而不尽其才。畏害于临乱之日而徒事全躯。其忘君背义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更何足论哉。静女
御制条问曰。强暴谓之吉士。野有死麇章有之。而其意欲使知愧耳。此章之以淫妇而谓之静女。何哉。是爱而不知其恶。如所谓心所恬而素亦缣者欤。然静非性静之谓。乃容静之谓。其貌閒雅而心志则乱耳。然而欧阳公以为幽静难诱之女且然。有若本有幽静之德而今却媮污者然。岂先贞后黩。如后世河间淫妇者欤。
臣对曰。相与之淫。其情可知其爱好矣。相与之赞。其辞可知其嘉美矣。爱好之极。不知其恶。故赞美之辞。不期而然。复安有性静貌静之暇论哉。见朱子德音之卞。益可验也。臣于汉广之诗。见女子革其淫乱游冶之俗。化为幽閒庄静之仪。以此知周德之广远也。及于静女之诗。见女子变其幽静难诱之习。转成邪淫媮污之态。以此知卫国之危乱也。此只在在上者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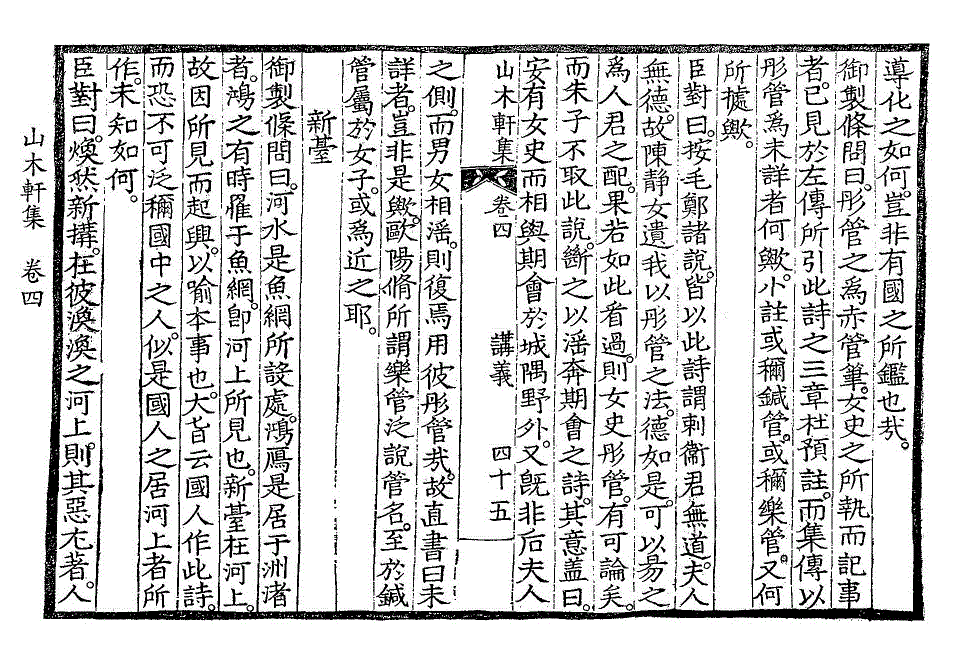 导化之如何。岂非有国之所鉴也哉。
导化之如何。岂非有国之所鉴也哉。御制条问曰。彤管之为赤管笔。女史之所执而记事者。已见于左传所引此诗之三章杜预注。而集传以彤管为未详者何欤。小注或称针管。或称乐管。又何所据欤。
臣对曰。按毛,郑诸说。皆以此诗谓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果若如此看过。则女史彤管。有可论矣。而朱子不取此说。断之以淫奔期会之诗。其意盖曰。安有女史而相与期会于城隅野外。又既非后夫人之侧。而男女相淫。则复焉用彼彤管哉。故直书曰未详者。岂非是欤。欧阳脩所谓乐管泛说管名。至于针管属于女子。或为近之耶。
新台
御制条问曰。河水是鱼网所设处。鸿雁是居于洲渚者。鸿之有时罹于鱼网。即河上所见也。新台在河上。故因所见而起兴。以喻本事也。大旨云国人作此诗。而恐不可泛称国中之人。似是国人之居河上者所作。未知如何。
臣对曰。焕然新搆。在彼涣涣之河上。则其恶尤著。人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3L 页
 之恶之而刺之也。固因河上之所见。而唯彼行路之人。所同者秉彝之心也。指顾眺望之间。莫不唾骂。则国人皆是也。虽非河上之人。独不作是诗耶。
之恶之而刺之也。固因河上之所见。而唯彼行路之人。所同者秉彝之心也。指顾眺望之间。莫不唾骂。则国人皆是也。虽非河上之人。独不作是诗耶。二子乘舟
御制条问曰。二子乘舟。疑其渡河而死也。然左传曰。杀于莘。又曰杀于隘。莘固河西而非踰河矣。隘亦非涉河之地也。史记曰。死于界上。界即自卫适齐之界。而隔河非渡河矣。左传,史记。皆无二子渡河事。而诗有乘舟之语。何欤。惟刘向新序。云宣公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沉而杀之。寿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之时。傅母恐其死也。闷而作诗。舟行无恙。其后未几。有使伋之齐。伋,寿并死之事。据此文则实有二子乘舟之事。然左传,史记之所无。刘向何所据而为之说如此欤。似是傅会诗文而云。不可取信。然则二子乘舟之事。无明證甚可疑。而朱子于大旨。初不说破。只引旧说。略书伋,寿事。而不言其所以乘舟之故。恐欠详备。未知何如。
臣对曰。毛传所谓隘也。左氏所谓莘也。史记所谓界也。同一其地。实无乘舟渡河之證。而毛氏释此诗。有曰国人伤其涉危而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以此观
山木轩集卷之四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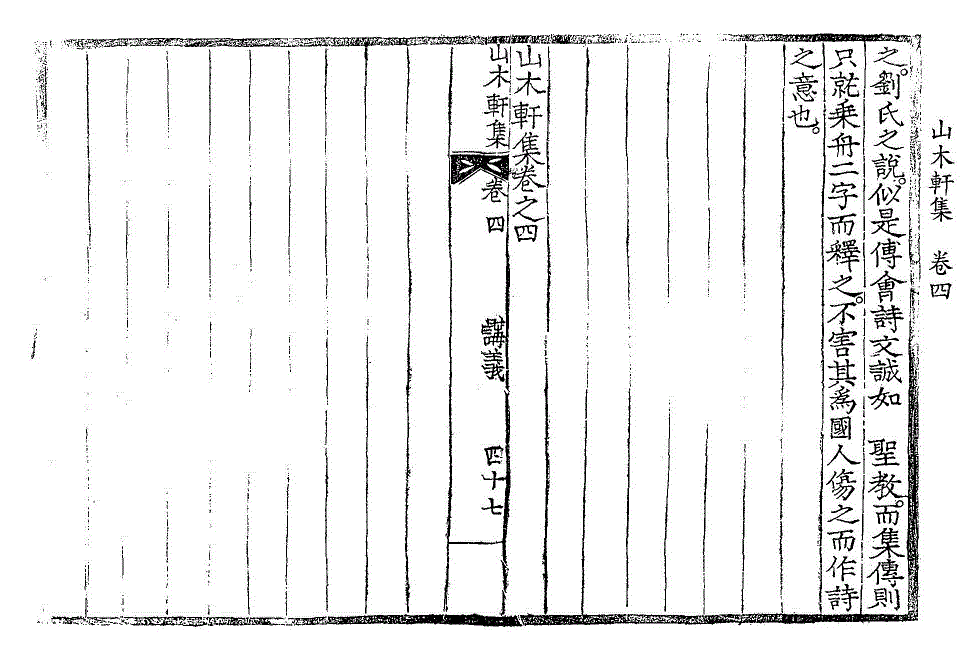 之。刘氏之说。似是傅会诗文诚如 圣教。而集传则只就乘舟二字而释之。不害其为国人伤之而作诗之意也。
之。刘氏之说。似是傅会诗文诚如 圣教。而集传则只就乘舟二字而释之。不害其为国人伤之而作诗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