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记
记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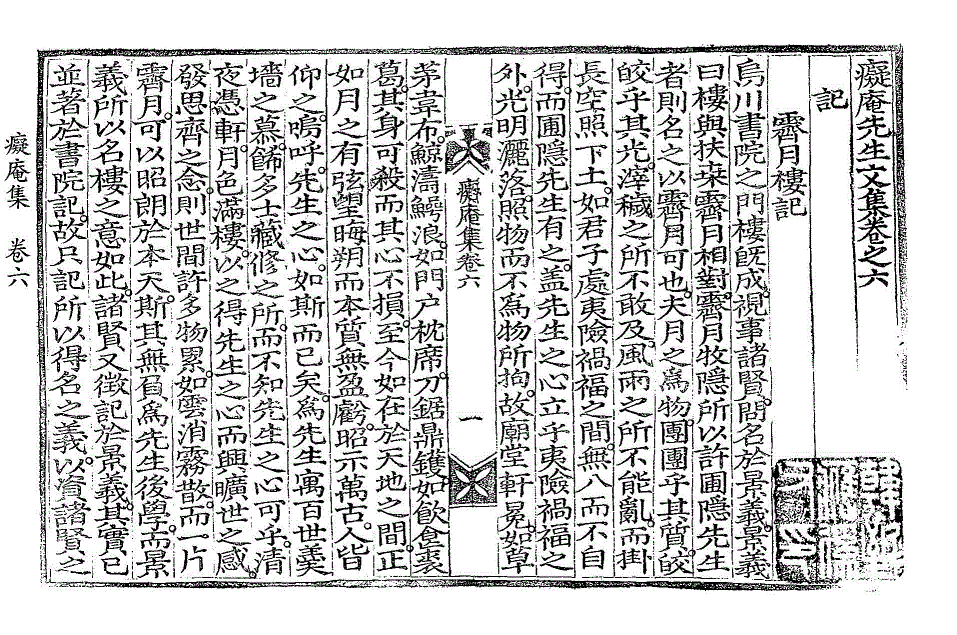 霁月楼记
霁月楼记乌川书院之门楼既成。视事诸贤。问名于景羲。景羲曰楼与扶桑霁月相对。霁月牧隐所以许圃隐先生者则名之以霁月可也。夫月之为物。团团乎其质。皎皎乎其光。滓秽之所不敢及。风雨之所不能乱。而挂长空照下土。如君子处夷险祸福之间。无入而不自得。而圃隐先生有之。盖先生之心立乎夷险祸福之外。光明洒落。照物而不为物所拘。故庙堂轩冕。如草茅韦布。鲸涛鳄浪。如门户枕席。刀锯鼎镬。如饮食裘葛。其身可杀而其心不损。至今如在于天地之间。正如月之有弦望晦朔而本质无盈亏。昭示万古。人皆仰之。呜呼。先生之心。如斯而已矣。为先生寓百世羹墙之慕。饰多士藏修之所。而不知先生之心可乎。清夜凭轩。月色满楼。以之得先生之心而兴旷世之感。发思齐之念。则世间许多物累。如云消雾散。而一片霁月。可以昭朗于本天。斯其无负为先生后学。而景羲所以名楼之意如此。诸贤又徵记于景羲。其实已并著于书院记。故只记所以得名之义。以资诸贤之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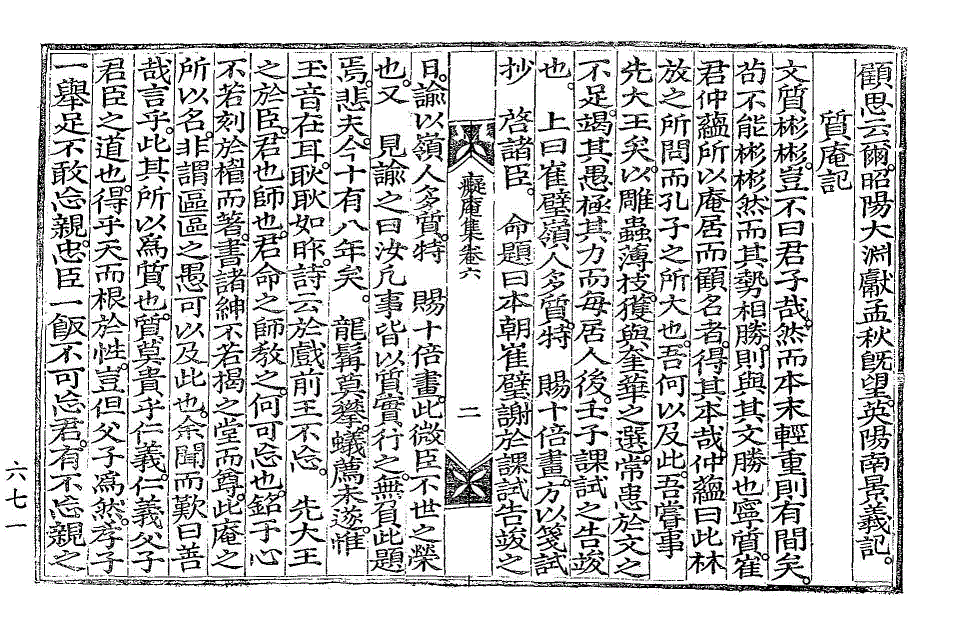 顾思云尔。昭阳大渊献孟秋既望。英阳南景羲记。
顾思云尔。昭阳大渊献孟秋既望。英阳南景羲记。质庵记
文质彬彬。岂不曰君子哉。然而本末轻重则有间矣。苟不能彬彬然而其势相胜。则与其文胜也宁质。崔君仲蕴所以庵居而顾名者。得其本哉。仲蕴曰此林放之所问而孔子之所大也。吾何以及此。吾尝事 先大王矣。以雕虫薄技。获与奎华之选。常患于文之不足。竭其愚极其力而每居人后。壬子课试之告竣也。 上曰崔璧岭人多质。特 赐十倍画。方以笺试抄 启诸臣。 命题曰本朝崔璧谢于课试告竣之日。谕以岭人多质。特 赐十倍画。此微臣不世之荣也。又 见谕之曰汝凡事皆以质实行之。无负此题焉。悲夫。今十有八年矣。 龙髯莫攀。蚁荐未遂。惟 玉音在耳。耿耿如昨。诗云于戏前王不忘。 先大王之于臣。君也师也。君命之师教之。何可忘也。铭于心不若刻于楣而著。书诸绅不若揭之堂而尊。此庵之所以名。非谓区区之愚可以及此也。余闻而叹曰善哉言乎。此其所以为质也。质莫贵乎仁义。仁义父子君臣之道也。得乎天而根于性。岂但父子为然。孝子一举足不敢忘亲。忠臣一饭不可忘君。有不忘亲之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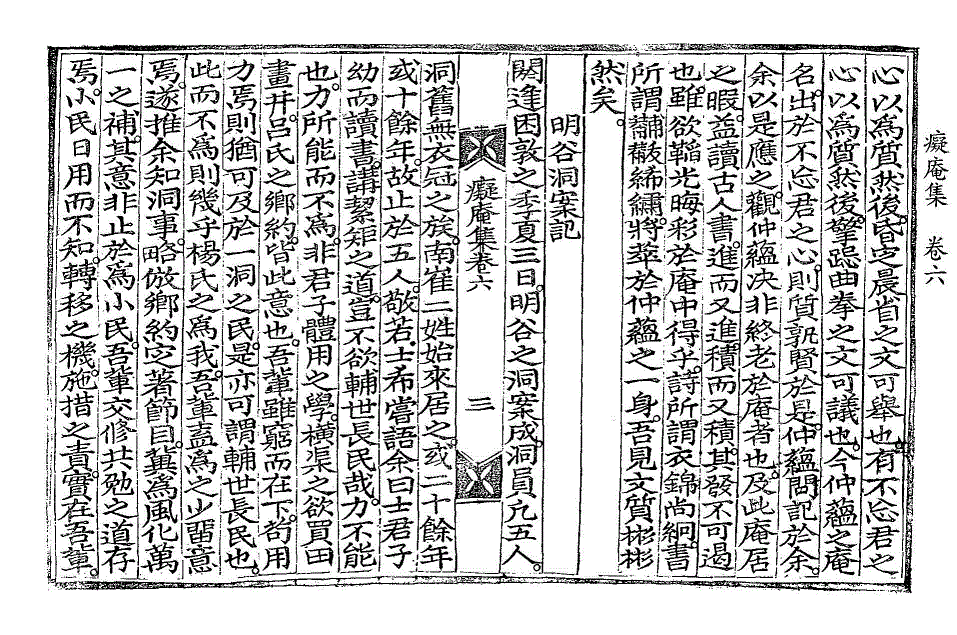 心以为质然后。昏定晨省之文可举也。有不忘君之心以为质然后。擎跽曲拳之文可议也。今仲蕴之庵名。出于不忘君之心。则质孰贤于是。仲蕴问记于余。余以是应之。观仲蕴决非终老于庵者也。及此庵居之暇。益读古人书。进而又进。积而又积。其发不可遏也。虽欲韬光晦彩于庵中得乎。诗所谓衣锦尚絅。书所谓黼黻絺绣。将萃于仲蕴之一身。吾见文质彬彬然矣。
心以为质然后。昏定晨省之文可举也。有不忘君之心以为质然后。擎跽曲拳之文可议也。今仲蕴之庵名。出于不忘君之心。则质孰贤于是。仲蕴问记于余。余以是应之。观仲蕴决非终老于庵者也。及此庵居之暇。益读古人书。进而又进。积而又积。其发不可遏也。虽欲韬光晦彩于庵中得乎。诗所谓衣锦尚絅。书所谓黼黻絺绣。将萃于仲蕴之一身。吾见文质彬彬然矣。明谷洞案记
阏逢困敦之季夏三日。明谷之洞案成。洞员凡五人。洞旧无衣冠之族。南崔二姓始来居之。或二十馀年或十馀年。故止于五人。敬若,士希尝语余曰士君子幼而读书。讲絜矩之道。岂不欲辅世长民哉。力不能也。力所能而不为。非君子体用之学。横渠之欲买田画井。吕氏之乡约。皆此意也。吾辈虽穷而在下。苟用力焉则犹可及于一洞之民。是亦可谓辅世长民也。此而不为则几乎杨氏之为我。吾辈盍为之少留意焉。遂推余知洞事。略仿乡约定著节目。冀为风化万一之补。其意非止于为小民。吾辈交修共勉之道存焉。小民日用而不知。转移之机。施措之责。实在吾辈。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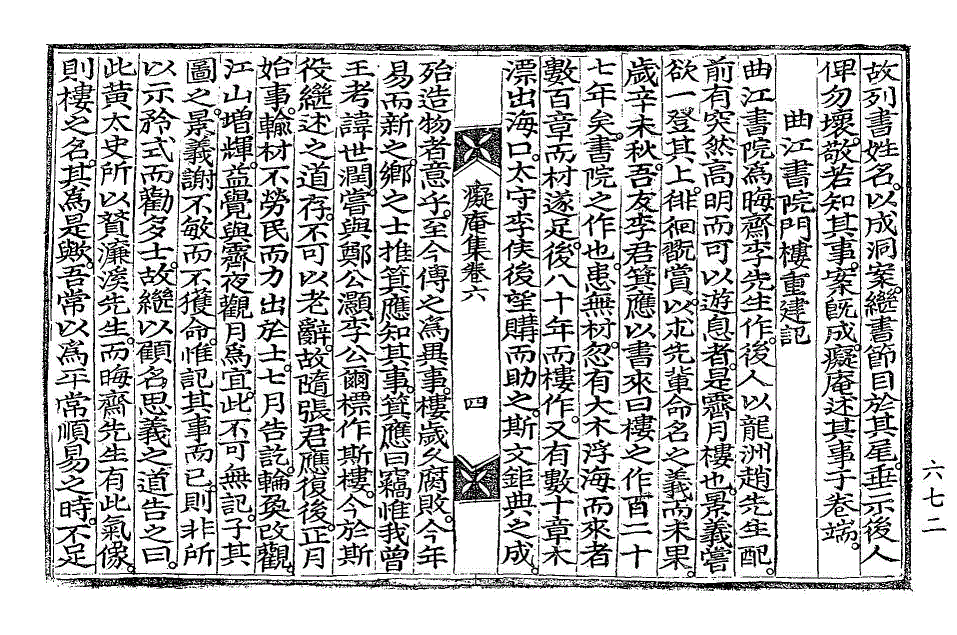 故列书姓名。以成洞案。继书节目于其尾。垂示后人俾勿坏。敬若知其事。案既成。痴庵述其事于卷端。
故列书姓名。以成洞案。继书节目于其尾。垂示后人俾勿坏。敬若知其事。案既成。痴庵述其事于卷端。曲江书院门楼重建记
曲江书院为晦斋李先生作。后人以龙洲赵先生配。前有突然高明而可以游息者。是霁月楼也。景羲尝欲一登其上。徘徊玩赏。以求先辈命名之义而未果。岁辛未秋。吾友李君箕应以书来曰楼之作百二十七年矣。书院之作也。患无材。忽有大木浮海而来者数百章而材遂足。后八十年而楼作。又有数十章木漂出海口。太守李侯后望购而助之。斯文钜典之成。殆造物者意乎。至今传之为异事。楼岁久腐败。今年易而新之。乡之士推箕应知其事。箕应曰窃惟我曾王考讳世润。尝与郑公灏,李公尔标作斯楼。今于斯役继述之道存。不可以老辞。故随张君应复后。正月始事。输材不劳民而力出于士。七月告讫。轮奂改观。江山增辉。益觉与霁夜观月为宜。此不可无记。子其图之。景羲谢不敏而不获命。惟记其事而已。则非所以示矜式而劝多士。故继以顾名思义之道告之曰。此黄太史所以赞濂溪先生。而晦斋先生有此气像。则楼之名。其为是欤。吾常以为平常顺易之时。不足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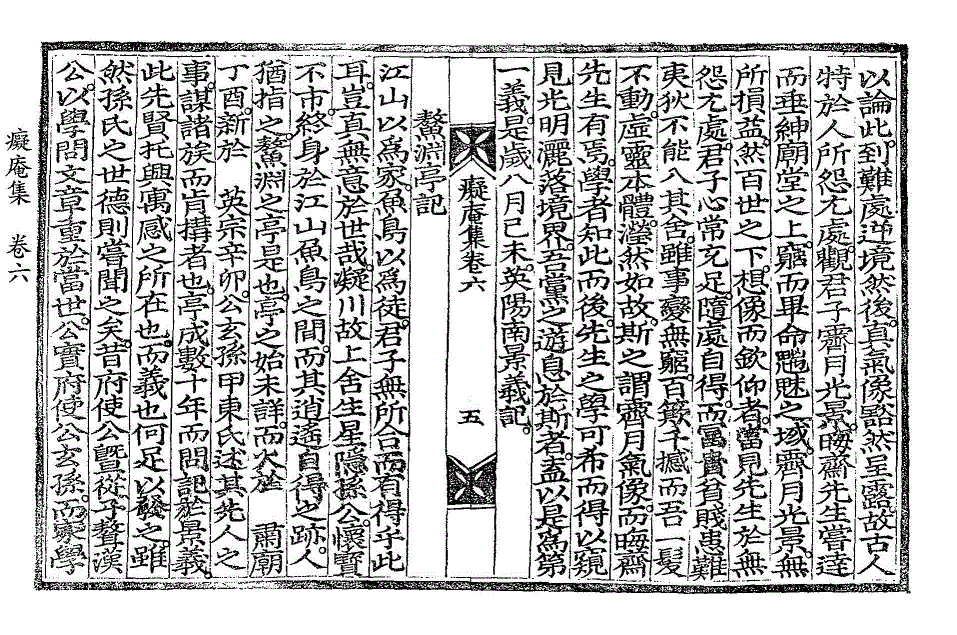 以论此。到难处逆境然后。真气像豁然呈露。故古人特于人所怨尤处。观君子霁月光景。晦斋先生尝达而垂绅庙堂之上。穷而毕命魑魅之域。霁月光景。无所损益。然百世之下。想像而钦仰者。当见先生于无怨尤处。君子心常充足。随处自得。而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不能入其舍。虽事变无穷。百𥳽千撼而吾一发不动。虚灵本体。滢然如故。斯之谓霁月气像。而晦斋先生有焉。学者知此而后。先生之学可希而得以窥见光明洒落境界。吾党之游息于斯者。盍以是为第一义。是岁八月己未。英阳南景羲记。
以论此。到难处逆境然后。真气像豁然呈露。故古人特于人所怨尤处。观君子霁月光景。晦斋先生尝达而垂绅庙堂之上。穷而毕命魑魅之域。霁月光景。无所损益。然百世之下。想像而钦仰者。当见先生于无怨尤处。君子心常充足。随处自得。而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不能入其舍。虽事变无穷。百𥳽千撼而吾一发不动。虚灵本体。滢然如故。斯之谓霁月气像。而晦斋先生有焉。学者知此而后。先生之学可希而得以窥见光明洒落境界。吾党之游息于斯者。盍以是为第一义。是岁八月己未。英阳南景羲记。鳌渊亭记
江山以为家。鱼鸟以为徒。君子无所合而有得乎此耳。岂真无意于世哉。凝川故上舍生星隐孙公。怀宝不市。终身于江山鱼鸟之间。而其逍遥自得之迹。人犹指之。鳌渊之亭是也。亭之始未详。而火于 肃庙丁酉。新于 英宗辛卯。公玄孙甲东氏述其先人之事。谋诸族而肯搆者也。亭成数十年而问记于景羲。此先贤托兴寓感之所在也。而羲也何足以发之。虽然孙氏之世德则尝闻之矣。昔府使公暨从子聱汉公。以学问文章重于当世。公实府使公玄孙。而家学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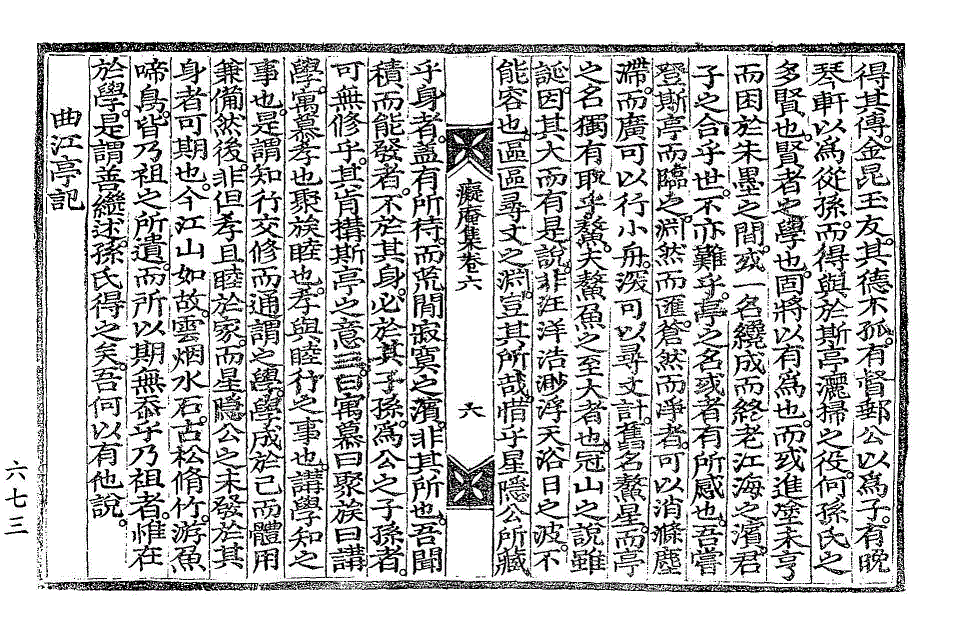 得其传。金昆玉友。其德不孤。有督邮公以为子。有晚琴轩以为从孙。而得与于斯亭洒扫之役。何孙氏之多贤也。贤者之学也。固将以有为也。而或进涂未亨而困于朱墨之间。或一名才成而终老江海之滨。君子之合乎世。不亦难乎。亭之名或者有所感也。吾尝登斯亭而临之。渊然而汇。苍然而净者。可以消涤尘滞。而广可以行小舟。深可以寻丈计。旧名鳌星。而亭之名独有取乎鳌。夫鳌鱼之至大者也。冠山之说虽诞。因其大而有是说。非汪洋浩渺浮天浴日之波。不能容也。区区寻丈之渊。岂其所哉。惜乎星隐公所藏乎身者。盖有所待。而荒閒寂寞之滨。非其所也。吾闻积而能发者。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为公之子孙者。可无修乎。其肯搆斯亭之意三。曰寓慕曰聚族曰讲学。寓慕孝也聚族睦也。孝与睦行之事也。讲学知之事也。是谓知行交修而通谓之学。学成于己而体用兼备然后。非但孝且睦于家。而星隐公之未发于其身者可期也。今江山如故。云烟水石。古松脩竹。游鱼啼鸟。皆乃祖之所遗。而所以期无忝乎乃祖者。惟在于学。是谓善继述。孙氏得之矣。吾何以有他说。
得其传。金昆玉友。其德不孤。有督邮公以为子。有晚琴轩以为从孙。而得与于斯亭洒扫之役。何孙氏之多贤也。贤者之学也。固将以有为也。而或进涂未亨而困于朱墨之间。或一名才成而终老江海之滨。君子之合乎世。不亦难乎。亭之名或者有所感也。吾尝登斯亭而临之。渊然而汇。苍然而净者。可以消涤尘滞。而广可以行小舟。深可以寻丈计。旧名鳌星。而亭之名独有取乎鳌。夫鳌鱼之至大者也。冠山之说虽诞。因其大而有是说。非汪洋浩渺浮天浴日之波。不能容也。区区寻丈之渊。岂其所哉。惜乎星隐公所藏乎身者。盖有所待。而荒閒寂寞之滨。非其所也。吾闻积而能发者。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为公之子孙者。可无修乎。其肯搆斯亭之意三。曰寓慕曰聚族曰讲学。寓慕孝也聚族睦也。孝与睦行之事也。讲学知之事也。是谓知行交修而通谓之学。学成于己而体用兼备然后。非但孝且睦于家。而星隐公之未发于其身者可期也。今江山如故。云烟水石。古松脩竹。游鱼啼鸟。皆乃祖之所遗。而所以期无忝乎乃祖者。惟在于学。是谓善继述。孙氏得之矣。吾何以有他说。曲江亭记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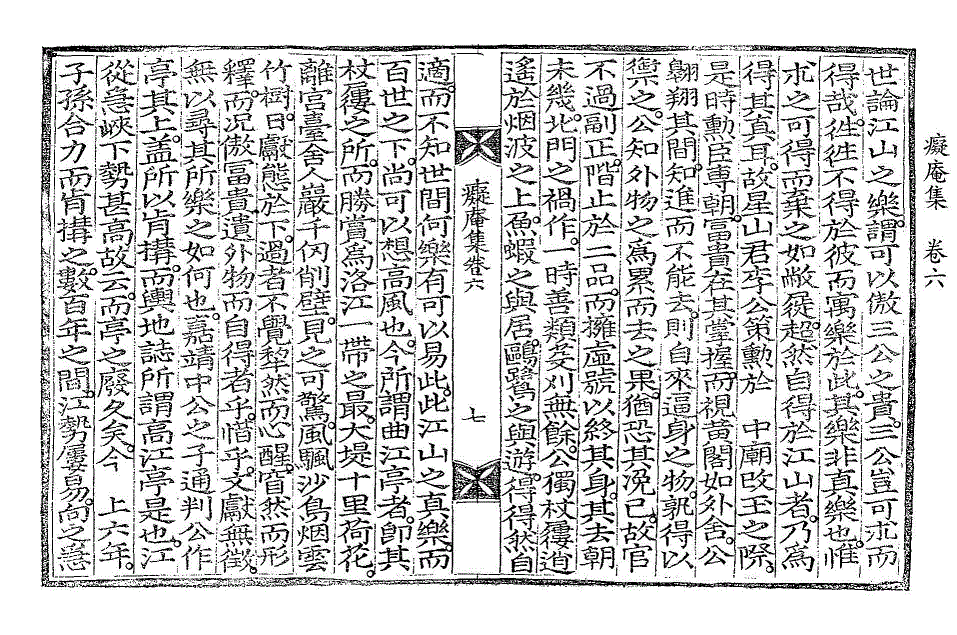 世论江山之乐。谓可以傲三公之贵。三公岂可求而得哉。往往不得于彼而寓乐于此。其乐非真乐也。惟求之可得而弃之如敝屣。超然自得于江山者。乃为得其真耳。故星山君李公策勋于 中庙改玉之际。是时勋臣专朝。富贵在其掌握。而视黄阁如外舍。公翱翔其间。知进而不能去。则自来逼身之物。孰得以御之。公知外物之为累而去之果。犹恐其浼己。故官不过副正。阶止于二品。而拥虚号以终其身。其去朝未几。北门之祸作。一时善类芟刈无馀。公独杖屦逍遥于烟波之上。鱼虾之与居。鸥鹭之与游。得得然自适。而不知世间何乐有可以易此。此江山之真乐。而百世之下。尚可以想高风也。今所谓曲江亭者。即其杖屦之所。而胜赏为洛江一带之最。大堤十里荷花。离宫台舍人岩千仞削壁。见之可惊。风帆沙鸟烟云竹树。日献态于下。过者不觉犁然而心醒。窅然而形释。而况傲富贵遗外物而自得者乎。惜乎。文献无徵。无以寻其所乐之如何也。嘉靖中公之子通判公作亭其上。盖所以肯搆。而舆地志所谓高江亭是也。江从急峡下势甚高故云。而亭之废久矣。今 上六年。子孙合力而肯搆之。数百年之间。江势屡易。向之急
世论江山之乐。谓可以傲三公之贵。三公岂可求而得哉。往往不得于彼而寓乐于此。其乐非真乐也。惟求之可得而弃之如敝屣。超然自得于江山者。乃为得其真耳。故星山君李公策勋于 中庙改玉之际。是时勋臣专朝。富贵在其掌握。而视黄阁如外舍。公翱翔其间。知进而不能去。则自来逼身之物。孰得以御之。公知外物之为累而去之果。犹恐其浼己。故官不过副正。阶止于二品。而拥虚号以终其身。其去朝未几。北门之祸作。一时善类芟刈无馀。公独杖屦逍遥于烟波之上。鱼虾之与居。鸥鹭之与游。得得然自适。而不知世间何乐有可以易此。此江山之真乐。而百世之下。尚可以想高风也。今所谓曲江亭者。即其杖屦之所。而胜赏为洛江一带之最。大堤十里荷花。离宫台舍人岩千仞削壁。见之可惊。风帆沙鸟烟云竹树。日献态于下。过者不觉犁然而心醒。窅然而形释。而况傲富贵遗外物而自得者乎。惜乎。文献无徵。无以寻其所乐之如何也。嘉靖中公之子通判公作亭其上。盖所以肯搆。而舆地志所谓高江亭是也。江从急峡下势甚高故云。而亭之废久矣。今 上六年。子孙合力而肯搆之。数百年之间。江势屡易。向之急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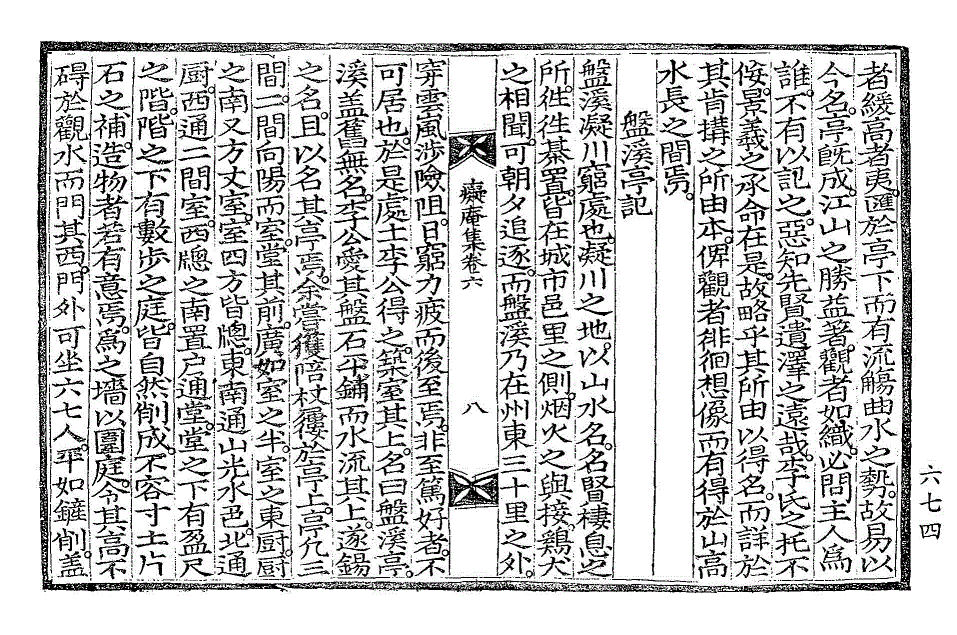 者缓高者夷。汇于亭下而有流觞曲水之势。故易以今名。亭既成。江山之胜益著。观者如织。必问主人为谁。不有以记之。恶知先贤遗泽之远哉。李氏之托不佞。景羲之承命在是。故略乎其所由以得名。而详于其肯搆之所由本。俾观者徘徊想像而有得于山高水长之间焉。
者缓高者夷。汇于亭下而有流觞曲水之势。故易以今名。亭既成。江山之胜益著。观者如织。必问主人为谁。不有以记之。恶知先贤遗泽之远哉。李氏之托不佞。景羲之承命在是。故略乎其所由以得名。而详于其肯搆之所由本。俾观者徘徊想像而有得于山高水长之间焉。盘溪亭记
盘溪凝川穷处也。凝川之地。以山水名。名贤栖息之所。往往棋置。皆在城市邑里之侧。烟火之与接。鸡犬之相闻。可朝夕追逐。而盘溪乃在州东三十里之外。穿云岚涉险阻。日穷力疲而后至焉。非至笃好者。不可居也。于是处士李公得之。筑室其上。名曰盘溪亭。溪盖旧无名。李公爱其盘石平铺而水流其上。遂锡之名。且以名其亭焉。余尝获陪杖屦于亭上。亭凡三间。二间向阳而室。堂其前。广如室之半。室之东厨。厨之南又方丈室。室四方皆窗。东南通山光水色。北通厨。西通二间室。西窗之南置户通堂。堂之下有盈尺之阶。阶之下有数步之庭。皆自然削成。不容寸土片石之补。造物者若有意焉。为之墙以围庭。令其高不碍于观水而门其西。门外可坐六七人。平如铲削。盖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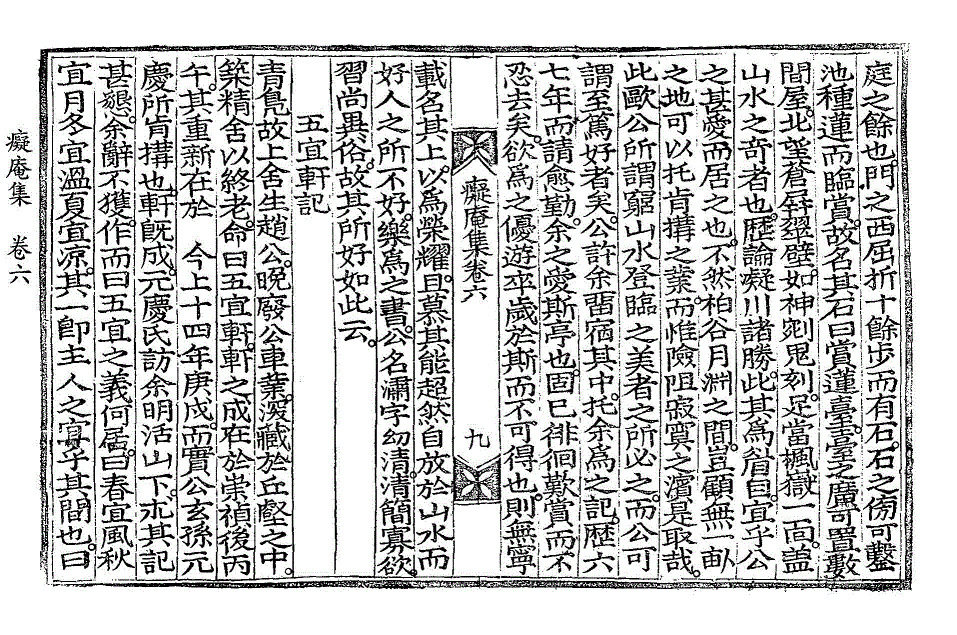 庭之馀也。门之西屈折十馀步而有石。石之傍可凿池种莲而临赏。故名其石曰赏莲台。台之广可置数间屋。北望苍屏翠壁。如神剜鬼刻。足当枫岳一面。盖山水之奇者也。历论凝川诸胜。此其为眉目。宜乎公之甚爱而居之也。不然柏谷月渊之间。岂顾无一亩之地可以托肯搆之业。而惟险阻寂寞之滨是取哉。此欧公所谓穷山水登临之美者之所必之。而公可谓至笃好者矣。公许余留宿其中。托余为之记。历六七年而请愈勤。余之爱斯亭也。固已徘徊叹赏而不忍去矣。欲为之优游卒岁于斯而不可得也。则无宁载名其上。以为荣耀。且慕其能超然自放于山水而好人之所不好。乐为之书。公名潚字幼清。清简寡欲。习尚异俗。故其所好如此云。
庭之馀也。门之西屈折十馀步而有石。石之傍可凿池种莲而临赏。故名其石曰赏莲台。台之广可置数间屋。北望苍屏翠壁。如神剜鬼刻。足当枫岳一面。盖山水之奇者也。历论凝川诸胜。此其为眉目。宜乎公之甚爱而居之也。不然柏谷月渊之间。岂顾无一亩之地可以托肯搆之业。而惟险阻寂寞之滨是取哉。此欧公所谓穷山水登临之美者之所必之。而公可谓至笃好者矣。公许余留宿其中。托余为之记。历六七年而请愈勤。余之爱斯亭也。固已徘徊叹赏而不忍去矣。欲为之优游卒岁于斯而不可得也。则无宁载名其上。以为荣耀。且慕其能超然自放于山水而好人之所不好。乐为之书。公名潚字幼清。清简寡欲。习尚异俗。故其所好如此云。五宜轩记
青凫故上舍生赵公。晚废公车业。深藏于丘壑之中。筑精舍以终老。命曰五宜轩。轩之成在于崇祯后丙午。其重新在于 今上十四年庚戌。而实公玄孙元庆所肯搆也。轩既成。元庆氏访余明活山下。求其记甚恳。余辞不获。作而曰五宜之义何居。曰春宜风秋宜月冬宜温夏宜凉。其一即主人之宜乎其间也。曰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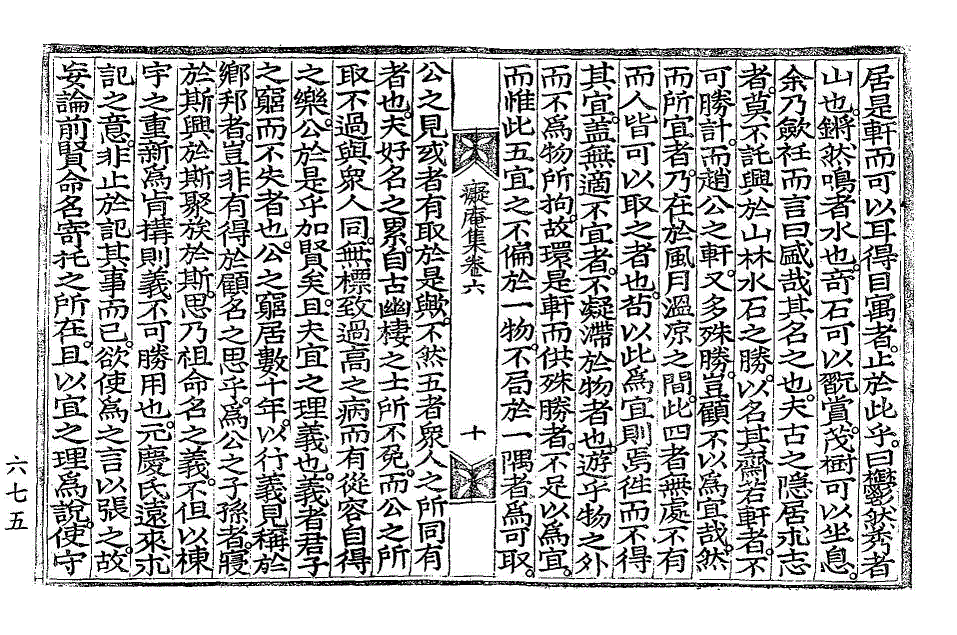 居是轩而可以耳得目寓者。止于此乎。曰郁然秀者山也。锵然鸣者水也。奇石可以玩赏。茂树可以坐息。余乃敛衽而言曰盛哉其名之也。夫古之隐居求志者。莫不托兴于山林水石之胜。以名其斋若轩者。不可胜计。而赵公之轩。又多殊胜。岂顾不以为宜哉。然而所宜者。乃在于风月温凉之间。此四者无处不有而人皆可以取之者也。苟以此为宜则焉往而不得其宜。盖无适不宜者。不凝滞于物者也。游乎物之外而不为物所拘。故环是轩而供殊胜者。不足以为宜。而惟此五宜之不偏于一物。不局于一隅者为可取。公之见或者有取于是欤。不然五者众人之所同有者也。夫好名之累。自古幽栖之士所不免。而公之所取不过与众人同。无标致过高之病而有从容自得之乐。公于是乎加贤矣。且夫宜之理义也。义者君子之穷而不失者也。公之穷居数十年。以行义见称于乡邦者。岂非有得于顾名之思乎。为公之子孙者。寝于斯兴于斯聚族于斯。思乃祖命名之义。不但以栋宇之重新为肯搆则义不可胜用也。元庆氏远来求记之意。非止于记其事而已。欲使为之言以张之。故妄论前贤命名寄托之所在。且以宜之理为说。使守
居是轩而可以耳得目寓者。止于此乎。曰郁然秀者山也。锵然鸣者水也。奇石可以玩赏。茂树可以坐息。余乃敛衽而言曰盛哉其名之也。夫古之隐居求志者。莫不托兴于山林水石之胜。以名其斋若轩者。不可胜计。而赵公之轩。又多殊胜。岂顾不以为宜哉。然而所宜者。乃在于风月温凉之间。此四者无处不有而人皆可以取之者也。苟以此为宜则焉往而不得其宜。盖无适不宜者。不凝滞于物者也。游乎物之外而不为物所拘。故环是轩而供殊胜者。不足以为宜。而惟此五宜之不偏于一物。不局于一隅者为可取。公之见或者有取于是欤。不然五者众人之所同有者也。夫好名之累。自古幽栖之士所不免。而公之所取不过与众人同。无标致过高之病而有从容自得之乐。公于是乎加贤矣。且夫宜之理义也。义者君子之穷而不失者也。公之穷居数十年。以行义见称于乡邦者。岂非有得于顾名之思乎。为公之子孙者。寝于斯兴于斯聚族于斯。思乃祖命名之义。不但以栋宇之重新为肯搆则义不可胜用也。元庆氏远来求记之意。非止于记其事而已。欲使为之言以张之。故妄论前贤命名寄托之所在。且以宜之理为说。使守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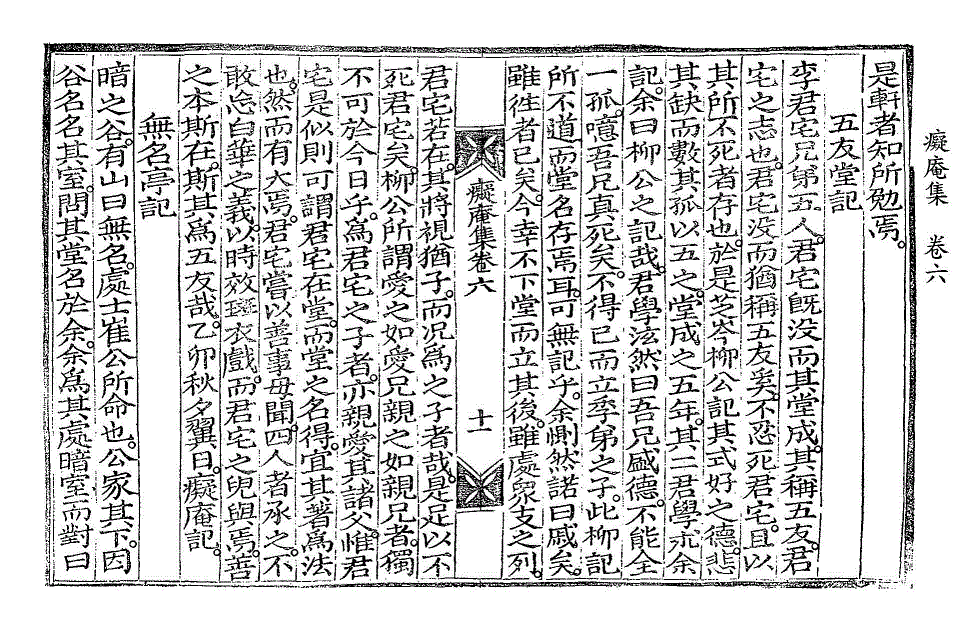 是轩者知所勉焉。
是轩者知所勉焉。五友堂记
李君宅兄弟五人。君宅既没而其堂成。其称五友。君宅之志也。君宅没而犹称五友奚。不忍死君宅。且以其所不死者存也。于是芝岑柳公记其式好之德。悲其缺而数其孤以五之。堂成之五年。其二君学求余记。余曰柳公之记哉。君学泫然曰吾兄盛德。不能全一孤。噫吾兄真死矣。不得已而立季弟之子。此柳记所不道而堂名存焉耳。可无记乎。余恻然诺曰戚矣。虽往者已矣。今幸不下堂而立其后。虽处众支之列。君宅若在。其将视犹子。而况为之子者哉。是足以不死君宅矣。柳公所谓爱之如爱兄亲之如亲兄者。独不可于今日乎。为君宅之子者。亦亲爱其诸父。惟君宅是似则可谓君宅在堂。而堂之名得。宜其著为法也。然而有大焉。君宅尝以善事母闻。四人者承之。不敢忘白华之义。以时效斑衣戏。而君宅之儿与焉。善之本斯在。斯其为五友哉。乙卯秋夕翼日。痴庵记。
无名亭记
暗之谷。有山曰无名。处士崔公所命也。公家其下。因谷名名其室。问其堂名于余。余为其处暗室而对曰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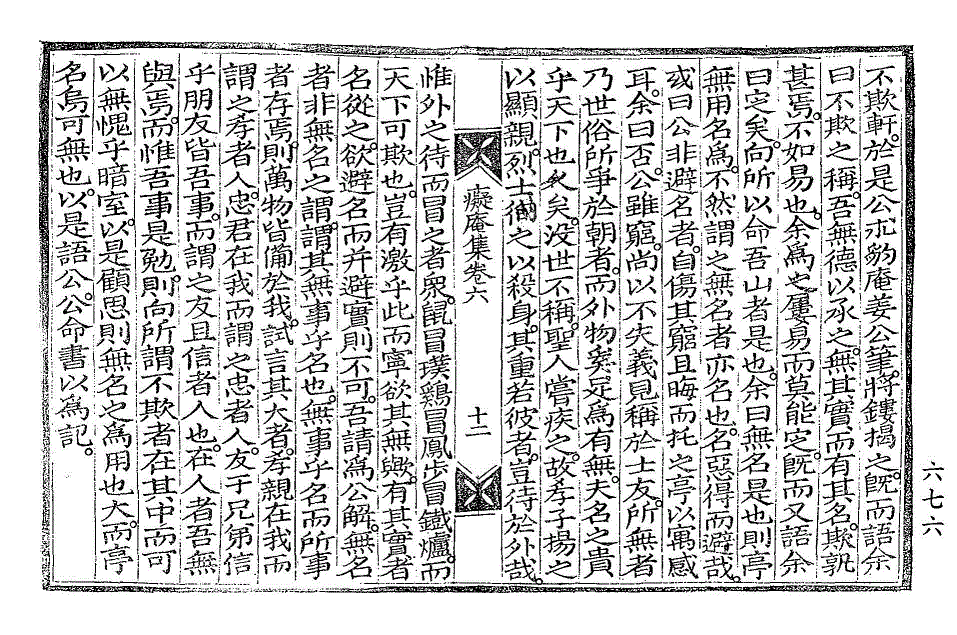 不欺轩。于是公求豹庵姜公笔。将镂揭之。既而语余曰不欺之称。吾无德以承之。无其实而有其名。欺孰甚焉。不如易也。余为之屡易而莫能定。既而又语余曰定矣。向所以命吾山者是也。余曰无名是也则亭无用名为。不然谓之无名者亦名也。名恶得而避哉。或曰公非避名者。自伤其穷且晦而托之亭以寓感耳。余曰否。公虽穷。尚以不失义见称于士友。所无者乃世俗所争于朝者。而外物奚足为有无。夫名之贵乎天下也久矣。没世不称。圣人尝疾之。故孝子扬之以显亲。烈士徇之以杀身。其重若彼者。岂待于外哉。惟外之待而冒之者众。鼠冒璞鸡冒凤步冒铁炉。而天下可欺也。岂有激乎此而宁欲其无欤。有其实者名从之。欲避名而并避实则不可。吾请为公解。无名者非无名之谓。谓其无事乎名也。无事乎名而所事者存焉。则万物皆备于我。试言其大者。孝亲在我而谓之孝者人。忠君在我而谓之忠者人。友于兄弟信乎朋友皆吾事。而谓之友且信者人也。在人者吾无与焉。而惟吾事是勉。则向所谓不欺者在其中而可以无愧乎暗室。以是顾思则无名之为用也大。而亭名乌可无也。以是语公。公命书以为记。
不欺轩。于是公求豹庵姜公笔。将镂揭之。既而语余曰不欺之称。吾无德以承之。无其实而有其名。欺孰甚焉。不如易也。余为之屡易而莫能定。既而又语余曰定矣。向所以命吾山者是也。余曰无名是也则亭无用名为。不然谓之无名者亦名也。名恶得而避哉。或曰公非避名者。自伤其穷且晦而托之亭以寓感耳。余曰否。公虽穷。尚以不失义见称于士友。所无者乃世俗所争于朝者。而外物奚足为有无。夫名之贵乎天下也久矣。没世不称。圣人尝疾之。故孝子扬之以显亲。烈士徇之以杀身。其重若彼者。岂待于外哉。惟外之待而冒之者众。鼠冒璞鸡冒凤步冒铁炉。而天下可欺也。岂有激乎此而宁欲其无欤。有其实者名从之。欲避名而并避实则不可。吾请为公解。无名者非无名之谓。谓其无事乎名也。无事乎名而所事者存焉。则万物皆备于我。试言其大者。孝亲在我而谓之孝者人。忠君在我而谓之忠者人。友于兄弟信乎朋友皆吾事。而谓之友且信者人也。在人者吾无与焉。而惟吾事是勉。则向所谓不欺者在其中而可以无愧乎暗室。以是顾思则无名之为用也大。而亭名乌可无也。以是语公。公命书以为记。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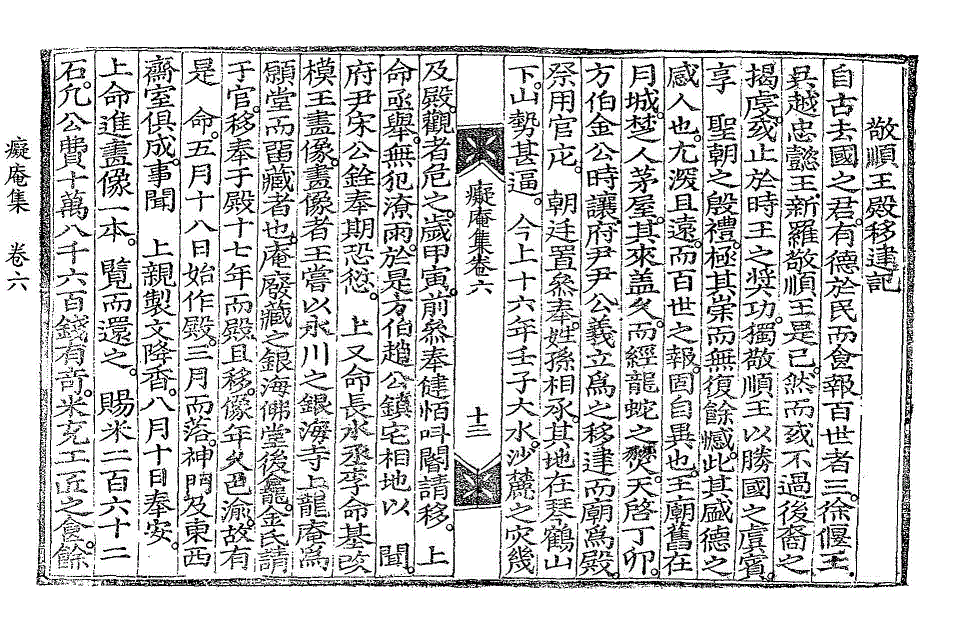 敬顺王殿移建记
敬顺王殿移建记自古去国之君。有德于民而食报百世者三。徐偃王,吴越忠懿王,新罗敬顺王是已。然而或不过后裔之揭虔。或止于时王之奖功。独敬顺王以胜国之虞宾。享 圣朝之殷礼。极其崇而无复馀憾。此其盛德之感人也。尤深且远。而百世之报。固自异也。王庙旧在月城。楚人茅屋。其来盖久。而经龙蛇之燹。天启丁卯。方伯金公时让,府尹尹公义立为之移建而庙为殿。祭用官庀。 朝廷置参奉。姓孙相承。其地在琴鹤山下。山势甚逼。 今上十六年壬子大水。沙麓之灾几及殿。观者危之。岁甲寅。前参奉健恒叫阍请移。 上命亟举。无犯潦雨。于是方伯赵公镇宅相地以 闻。府尹宋公铨奉期恐愆。 上又命长水丞李命基改模王画像。画像者王尝以永川之银海寺上龙庵为愿堂而留藏者也。庵废藏之银海佛堂后龛。金氏请于官。移奉于殿十七年而殿且移。像年久色渝。故有是 命。五月十八日始作殿。三月而落。神门及东西斋室俱成。事闻 上亲制文降香。八月十日奉安。 上命进画像一本。 览而还之。 赐米二百六十二石。凡公费十万八千六百钱有奇。米充工匠之食。馀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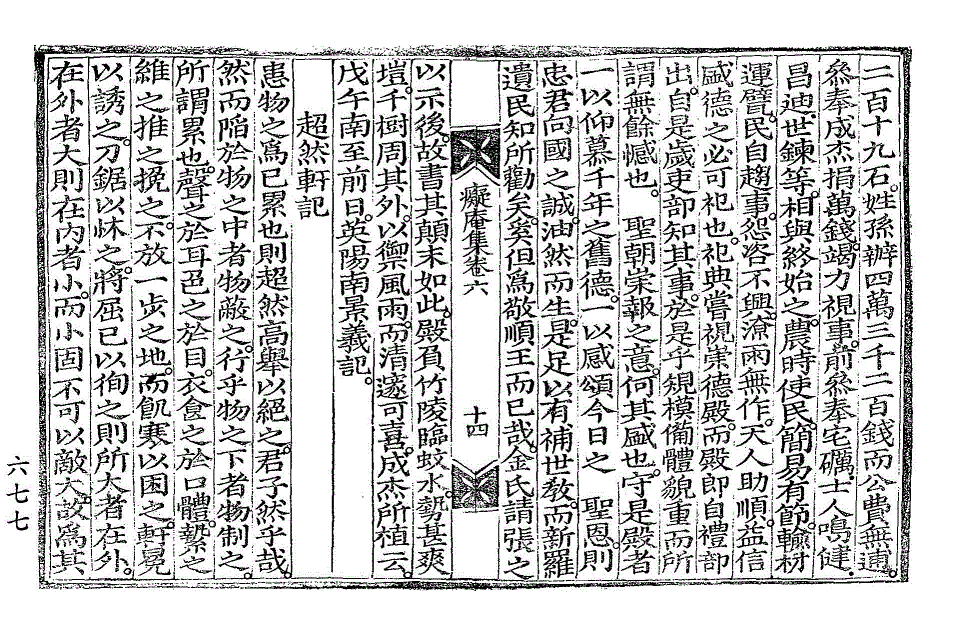 二百十九石。姓孙办四万三千二百钱而公费无逋。参奉成杰捐万钱。竭力视事。前参奉宅砺,士人鸣健,昌迪,世鍊等。相与终始之。农时使民。简易有节。输材运甓。民自趋事。怨咨不兴。潦雨无作。天人助顺。益信盛德之必可祀也。祀典尝视崇德殿。而殿郎自礼部出。自是岁吏部知其事。于是乎规模备体貌重而所谓无馀憾也。 圣朝崇报之意。何其盛也。守是殿者一以仰慕千年之旧德。一以感颂今日之 圣恩。则忠君向国之诚。油然而生。是足以有补世教。而新罗遗民知所劝矣。奚但为敬顺王而已哉。金氏请张之以示后。故书其颠末如此。殿负竹陵临蚊水。势甚爽垲。千树周其外。以御风雨。而清邃可喜。成杰所植云。戊午南至前日。英阳南景羲记。
二百十九石。姓孙办四万三千二百钱而公费无逋。参奉成杰捐万钱。竭力视事。前参奉宅砺,士人鸣健,昌迪,世鍊等。相与终始之。农时使民。简易有节。输材运甓。民自趋事。怨咨不兴。潦雨无作。天人助顺。益信盛德之必可祀也。祀典尝视崇德殿。而殿郎自礼部出。自是岁吏部知其事。于是乎规模备体貌重而所谓无馀憾也。 圣朝崇报之意。何其盛也。守是殿者一以仰慕千年之旧德。一以感颂今日之 圣恩。则忠君向国之诚。油然而生。是足以有补世教。而新罗遗民知所劝矣。奚但为敬顺王而已哉。金氏请张之以示后。故书其颠末如此。殿负竹陵临蚊水。势甚爽垲。千树周其外。以御风雨。而清邃可喜。成杰所植云。戊午南至前日。英阳南景羲记。超然轩记
患物之为己累也则超然高举以绝之。君子然乎哉。然而陷于物之中者物蔽之。行乎物之下者物制之。所谓累也。声之于耳色之于目。衣食之于口体。絷之维之推之挽之。不放一步之地。而饥寒以困之。轩冕以诱之。刀锯以怵之。将屈己以徇之则所大者在外。在外者大则在内者小。而小固不可以敌大。故为其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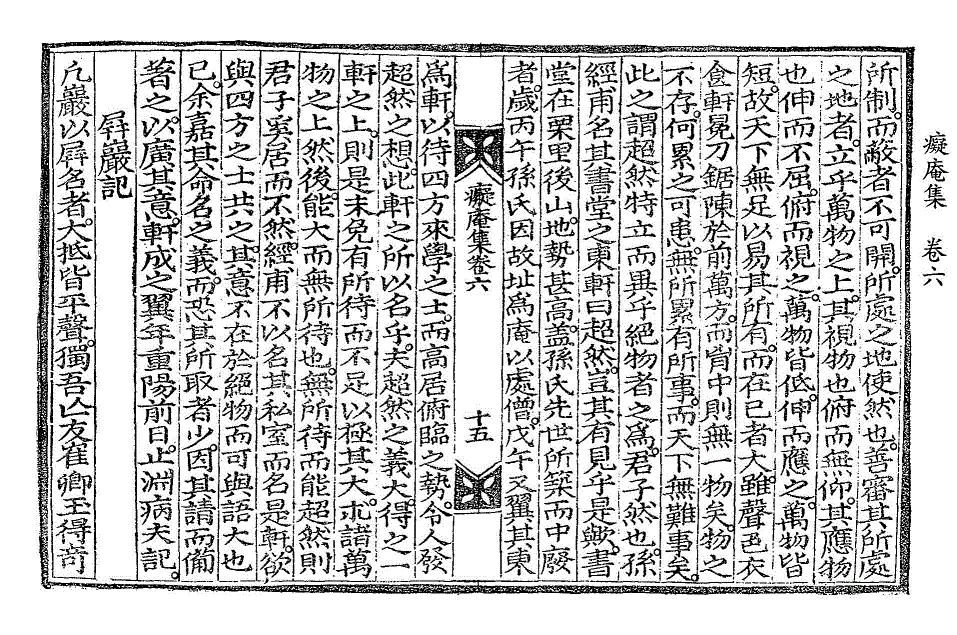 所制。而蔽者不可开。所处之地使然也。善审其所处之地者。立乎万物之上。其视物也俯而无仰。其应物也伸而不屈。俯而视之。万物皆低。伸而应之。万物皆短。故天下无足以易其所有。而在己者大。虽声色衣食轩冕刀锯陈于前万方。而胸中则无一物矣。物之不存。何累之可患。无所累有所事。而天下无难事矣。此之谓超然特立而异乎绝物者之为。君子然也。孙经甫名其书堂之东轩曰超然。岂其有见乎是欤。书堂在栗里后山。地势甚高。盖孙氏先世所筑而中废者。岁丙午孙氏因故址为庵以处僧。戊午又翼其东为轩。以待四方来学之士。而高居俯临之势。令人发超然之想。此轩之所以名乎。夫超然之义大。得之一轩之上。则是未免有所待而不足以极其大。求诸万物之上然后。能大而无所待也。无所待而能超然则君子奚居而不然。经甫不以名其私室而名是轩。欲与四方之士共之。其意不在于绝物而可与语大也已。余嘉其命名之义。而恐其所取者少。因其请而备著之。以广其意。轩成之翼年重阳前日。止渊病夫记。
所制。而蔽者不可开。所处之地使然也。善审其所处之地者。立乎万物之上。其视物也俯而无仰。其应物也伸而不屈。俯而视之。万物皆低。伸而应之。万物皆短。故天下无足以易其所有。而在己者大。虽声色衣食轩冕刀锯陈于前万方。而胸中则无一物矣。物之不存。何累之可患。无所累有所事。而天下无难事矣。此之谓超然特立而异乎绝物者之为。君子然也。孙经甫名其书堂之东轩曰超然。岂其有见乎是欤。书堂在栗里后山。地势甚高。盖孙氏先世所筑而中废者。岁丙午孙氏因故址为庵以处僧。戊午又翼其东为轩。以待四方来学之士。而高居俯临之势。令人发超然之想。此轩之所以名乎。夫超然之义大。得之一轩之上。则是未免有所待而不足以极其大。求诸万物之上然后。能大而无所待也。无所待而能超然则君子奚居而不然。经甫不以名其私室而名是轩。欲与四方之士共之。其意不在于绝物而可与语大也已。余嘉其命名之义。而恐其所取者少。因其请而备著之。以广其意。轩成之翼年重阳前日。止渊病夫记。屏岩记
凡岩以屏名者。大抵皆平声。独吾亡友崔卿玉得奇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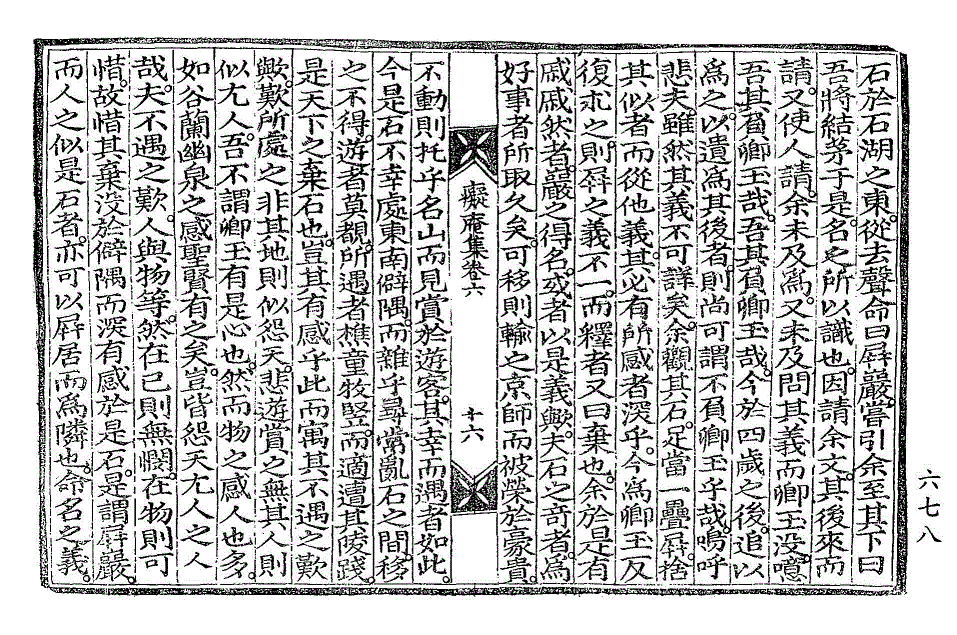 石于石湖之东。从去声命曰屏岩。尝引余至其下曰吾将结茅于是。名之所以识也。因请余文。其后来而请。又使人请。余未及为。又未及问其义而卿玉没。噫吾其负卿玉哉。吾其负卿玉哉。今于四岁之后。追以为之。以遗为其后者。则尚可谓不负卿玉乎哉。呜呼悲夫。虽然其义不可详矣。余观其石。足当一叠屏。舍其似者而从他义。其必有所感者深乎。今为卿玉反复求之。则屏之义不一。而释者又曰弃也。余于是有戚戚然者。岩之得名。或者以是义欤。夫石之奇者。为好事者所取久矣。可移则输之京师而被荣于豪贵。不动则托乎名山而见赏于游客。其幸而遇者如此。今是石不幸处东南僻隅。而杂乎寻常乱石之间。移之不得。游者莫睹。所遇者樵童牧竖。而适遭其陵践。是天下之弃石也。岂其有感乎此而寓其不遇之叹欤。叹所处之非其地则似怨天。悲游赏之无其人则似尤人。吾不谓卿玉有是心也。然而物之感人也多。如谷兰幽泉之感圣贤有之矣。岂皆怨天尤人之人哉。夫不遇之叹。人与物等。然在己则无悯。在物则可惜。故惜其弃没于僻隅而深有感于是石。是谓屏岩。而人之似是石者。亦可以屏居而为邻也。命名之义。
石于石湖之东。从去声命曰屏岩。尝引余至其下曰吾将结茅于是。名之所以识也。因请余文。其后来而请。又使人请。余未及为。又未及问其义而卿玉没。噫吾其负卿玉哉。吾其负卿玉哉。今于四岁之后。追以为之。以遗为其后者。则尚可谓不负卿玉乎哉。呜呼悲夫。虽然其义不可详矣。余观其石。足当一叠屏。舍其似者而从他义。其必有所感者深乎。今为卿玉反复求之。则屏之义不一。而释者又曰弃也。余于是有戚戚然者。岩之得名。或者以是义欤。夫石之奇者。为好事者所取久矣。可移则输之京师而被荣于豪贵。不动则托乎名山而见赏于游客。其幸而遇者如此。今是石不幸处东南僻隅。而杂乎寻常乱石之间。移之不得。游者莫睹。所遇者樵童牧竖。而适遭其陵践。是天下之弃石也。岂其有感乎此而寓其不遇之叹欤。叹所处之非其地则似怨天。悲游赏之无其人则似尤人。吾不谓卿玉有是心也。然而物之感人也多。如谷兰幽泉之感圣贤有之矣。岂皆怨天尤人之人哉。夫不遇之叹。人与物等。然在己则无悯。在物则可惜。故惜其弃没于僻隅而深有感于是石。是谓屏岩。而人之似是石者。亦可以屏居而为邻也。命名之义。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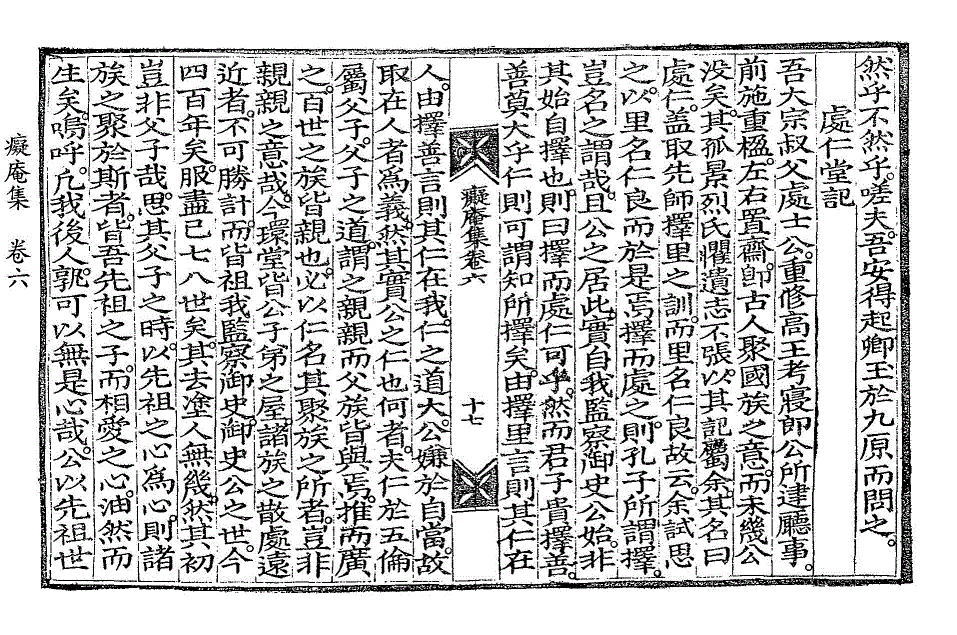 然乎不然乎。嗟夫。吾安得起卿玉于九原而问之。
然乎不然乎。嗟夫。吾安得起卿玉于九原而问之。处仁堂记
吾大宗叔父处士公。重修高王考寝郎公所建厅事。前施重楹。左右置斋。即古人聚国族之意。而未几公没矣。其孤景烈氏惧遗志不张。以其记属余。其名曰处仁。盖取先师择里之训。而里名仁良故云。余试思之。以里名仁良而于是焉择而处之。则孔子所谓择。岂名之谓哉。且公之居此。实自我监察御史公始。非其始自择也。则曰择而处仁可乎。然而君子贵择善。善莫大乎仁则可谓知所择矣。由择里言则其仁在人。由择善言则其仁在我。仁之道大。公嫌于自当。故取在人者为义。然其实公之仁也何者。夫仁于五伦属父子。父子之道。谓之亲亲而父族皆与焉。推而广之。百世之族皆亲也。必以仁名其聚族之所者。岂非亲亲之意哉。今环堂皆公子弟之屋。诸族之散处远近者。不可胜计。而皆祖我监察御史。御史公之世。今四百年矣。服尽已七八世矣。其去涂人无几。然其初岂非父子哉。思其父子之时。以先祖之心为心。则诸族之聚于斯者。皆吾先祖之子。而相爱之心。油然而生矣。呜呼。凡我后人。孰可以无是心哉。公以先祖世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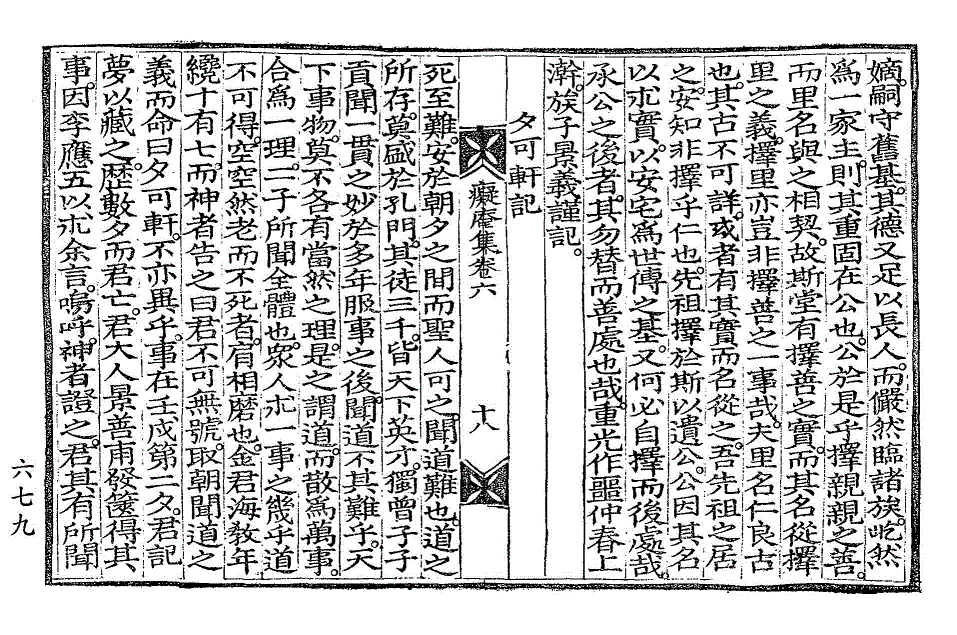 嫡。嗣守旧基。其德又足以长人。而俨然临诸族。屹然为一家主。则其重固在公也。公于是乎择亲亲之善。而里名与之相契。故斯堂有择善之实。而其名从择里之义。择里亦岂非择善之一事哉。夫里名仁良古也。其古不可详。或者有其实而名从之。吾先祖之居之。安知非择乎仁也。先祖择于斯以遗公。公因其名以求实。以安宅为世传之基。又何必自择而后处哉。承公之后者。其勿替而善处也哉。重光作噩仲春上浣。族子景羲谨记。
嫡。嗣守旧基。其德又足以长人。而俨然临诸族。屹然为一家主。则其重固在公也。公于是乎择亲亲之善。而里名与之相契。故斯堂有择善之实。而其名从择里之义。择里亦岂非择善之一事哉。夫里名仁良古也。其古不可详。或者有其实而名从之。吾先祖之居之。安知非择乎仁也。先祖择于斯以遗公。公因其名以求实。以安宅为世传之基。又何必自择而后处哉。承公之后者。其勿替而善处也哉。重光作噩仲春上浣。族子景羲谨记。夕可轩记
死至难。安于朝夕之间而圣人可之。闻道难也。道之所存。莫盛于孔门。其徒三千。皆天下英才。独曾子子贡闻一贯之妙于多年服事之后。闻道不其难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是之谓道。而散为万事。合为一理。二子所闻全体也。众人求一事之几乎道不可得。空空然老而不死者。肩相磨也。金君海教年才十有七。而神者告之曰君不可无号。取朝闻道之义而命曰夕可轩。不亦异乎。事在壬戌第二夕。君记梦以藏之。历数夕而君亡。君大人景善甫发箧得其事。因李应五以求余言。呜呼。神者證之。君其有所闻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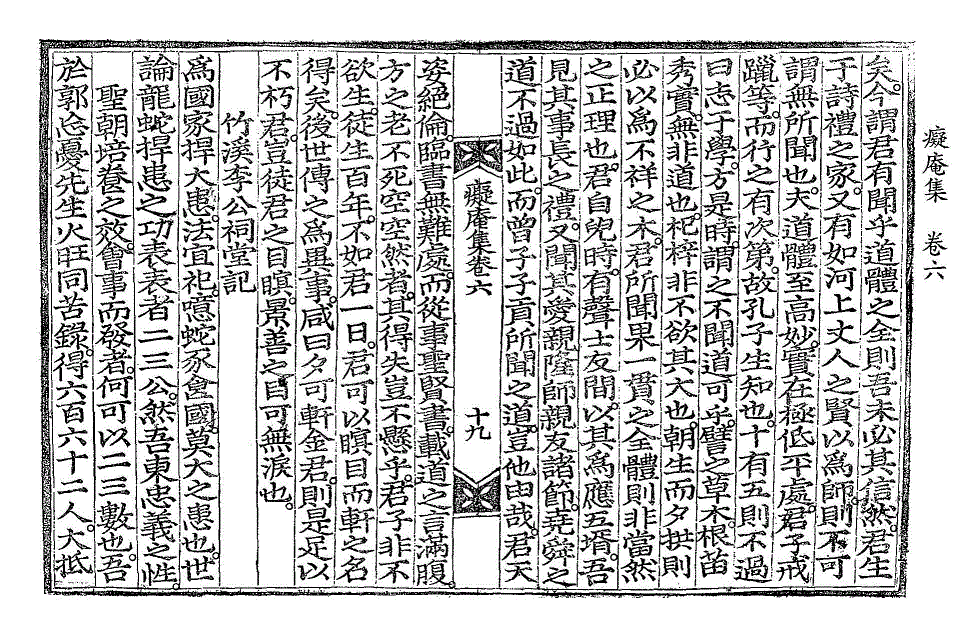 矣。今谓君有闻乎道体之全则吾未必其信然。君生于诗礼之家。又有如河上丈人之贤以为师。则不可谓无所闻也。夫道体至高妙。实在极低平处。君子戒躐等。而行之有次第。故孔子生知也。十有五则不过曰志于学。方是时。谓之不闻道可乎。譬之草木。根苗秀实。无非道也。杞梓非不欲其大也。朝生而夕拱则必以为不祥之木。君所闻果一贯之全体则非当然之正理也。君自儿时。有声士友间。以其为应五婿。吾见其事长之礼。又闻其爱亲隆师亲友诸节。尧舜之道不过如此。而曾子子贡所闻之道。岂他由哉。君天姿绝伦。临书无难处。而从事圣贤书。载道之言满腹。方之老不死空空然者。其得失岂不悬乎。君子非不欲生。徒生百年。不如君一日。君可以瞑目而轩之名得矣。后世传之为异事。咸曰夕可轩金君。则是足以不朽君。岂徒君之目瞑。景善之目可无泪也。
矣。今谓君有闻乎道体之全则吾未必其信然。君生于诗礼之家。又有如河上丈人之贤以为师。则不可谓无所闻也。夫道体至高妙。实在极低平处。君子戒躐等。而行之有次第。故孔子生知也。十有五则不过曰志于学。方是时。谓之不闻道可乎。譬之草木。根苗秀实。无非道也。杞梓非不欲其大也。朝生而夕拱则必以为不祥之木。君所闻果一贯之全体则非当然之正理也。君自儿时。有声士友间。以其为应五婿。吾见其事长之礼。又闻其爱亲隆师亲友诸节。尧舜之道不过如此。而曾子子贡所闻之道。岂他由哉。君天姿绝伦。临书无难处。而从事圣贤书。载道之言满腹。方之老不死空空然者。其得失岂不悬乎。君子非不欲生。徒生百年。不如君一日。君可以瞑目而轩之名得矣。后世传之为异事。咸曰夕可轩金君。则是足以不朽君。岂徒君之目瞑。景善之目可无泪也。竹溪李公祠堂记
为国家捍大患。法宜祀。噫蛇豕食国。莫大之患也。世论龙蛇捍患之功表表者二三公。然吾东忠义之性。 圣朝培养之效。会事而发者。何可以二三数也。吾于郭忘忧先生火旺同苦录。得六百六十二人。大抵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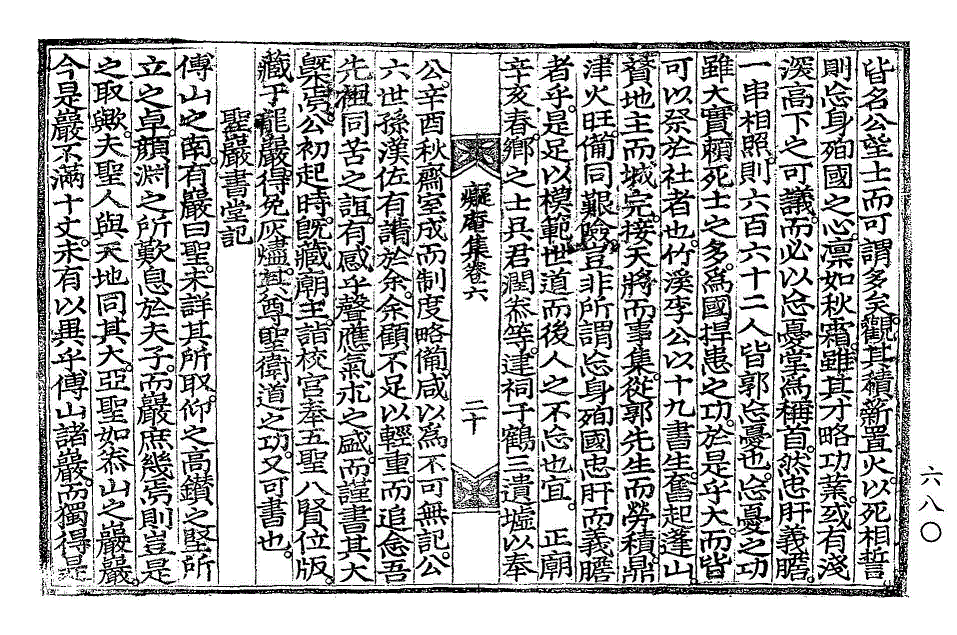 皆名公望士而可谓多矣。观其积薪置火。以死相誓。则忘身殉国之心。凛如秋霜。虽其才略功业。或有浅深高下之可议。而必以忘忧堂为称首。然忠肝义胆。一串相照。则六百六十二人皆郭忘忧也。忘忧之功虽大。实赖死士之多。为国捍患之功。于是乎大。而皆可以祭于社者也。竹溪李公以十九书生。奋起蓬山。赞地主而城完。接天将而事集。从郭先生而劳积。鼎津火旺。备同艰险。岂非所谓忘身殉国忠肝而义胆者乎。是足以模范世道而后人之不忘也宜。 正庙辛亥春。乡之士吴君润泰等。建祠于鹤三遗墟以奉公。辛酉秋斋室成而制度略备。咸以为不可无记。公六世孙汉佐有请于余。余顾不足以轻重。而追念吾先祖同苦之谊。有感乎声应气求之盛。而谨书其大槩焉。公初起时。既藏庙主。诣校宫奉五圣八贤位版。藏于龙岩。得免灰烬。其尊圣卫道之功。又可书也。
皆名公望士而可谓多矣。观其积薪置火。以死相誓。则忘身殉国之心。凛如秋霜。虽其才略功业。或有浅深高下之可议。而必以忘忧堂为称首。然忠肝义胆。一串相照。则六百六十二人皆郭忘忧也。忘忧之功虽大。实赖死士之多。为国捍患之功。于是乎大。而皆可以祭于社者也。竹溪李公以十九书生。奋起蓬山。赞地主而城完。接天将而事集。从郭先生而劳积。鼎津火旺。备同艰险。岂非所谓忘身殉国忠肝而义胆者乎。是足以模范世道而后人之不忘也宜。 正庙辛亥春。乡之士吴君润泰等。建祠于鹤三遗墟以奉公。辛酉秋斋室成而制度略备。咸以为不可无记。公六世孙汉佐有请于余。余顾不足以轻重。而追念吾先祖同苦之谊。有感乎声应气求之盛。而谨书其大槩焉。公初起时。既藏庙主。诣校宫奉五圣八贤位版。藏于龙岩。得免灰烬。其尊圣卫道之功。又可书也。圣岩书堂记
傅山之南。有岩曰圣。未详其所取。仰之高钻之坚所立之卓。颜渊之所叹息于夫子。而岩庶几焉则岂是之取欤。夫圣人与天地同其大。亚圣如泰山之岩岩。今是岩不满十丈。未有以异乎傅山诸岩。而独得是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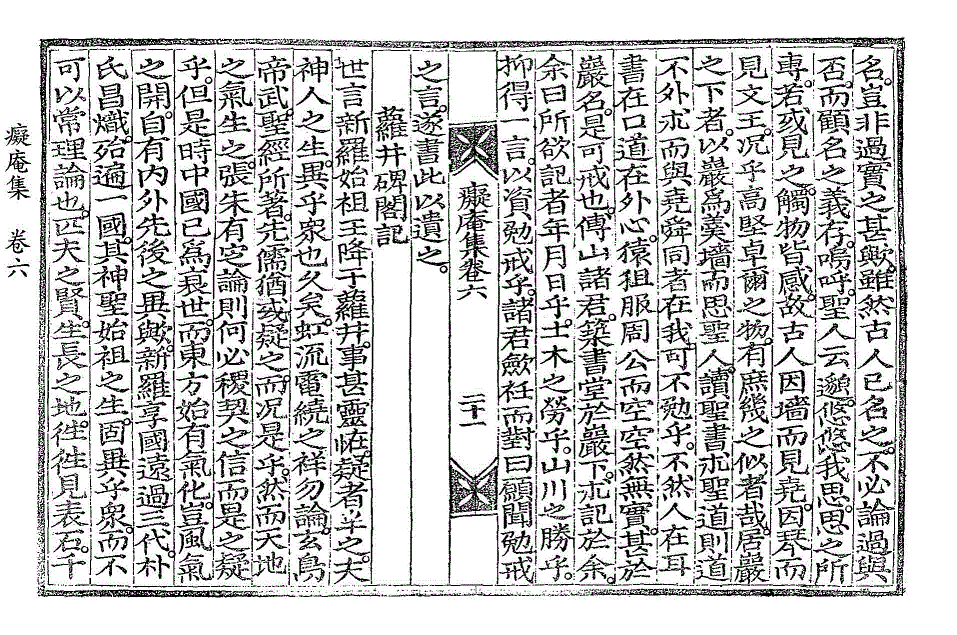 名。岂非过实之甚欤。虽然古人已名之。不必论过与否。而顾名之义存。呜呼。圣人云邈。悠悠我思。思之所专。若或见之。触物皆感。故古人因墙而见尧。因琴而见文王。况乎高坚卓尔之物。有庶几之似者哉。居岩之下者。以岩为羹墙而思圣人。读圣书求圣道则道不外求而与尧舜同者在我。可不勉乎。不然人在耳书在口道在外心。猿狙服周公而空空然无实。甚于岩名。是可戒也。傅山诸君。筑书堂于岩下。求记于余。余曰所欲记者年月日乎。土木之劳乎。山川之胜乎。抑得一言。以资勉戒乎。诸君敛衽而对曰愿闻勉戒之言。遂书此以遗之。
名。岂非过实之甚欤。虽然古人已名之。不必论过与否。而顾名之义存。呜呼。圣人云邈。悠悠我思。思之所专。若或见之。触物皆感。故古人因墙而见尧。因琴而见文王。况乎高坚卓尔之物。有庶几之似者哉。居岩之下者。以岩为羹墙而思圣人。读圣书求圣道则道不外求而与尧舜同者在我。可不勉乎。不然人在耳书在口道在外心。猿狙服周公而空空然无实。甚于岩名。是可戒也。傅山诸君。筑书堂于岩下。求记于余。余曰所欲记者年月日乎。土木之劳乎。山川之胜乎。抑得一言。以资勉戒乎。诸君敛衽而对曰愿闻勉戒之言。遂书此以遗之。萝井碑阁记
世言新罗始祖王降于萝井。事甚灵怪。疑者半之。夫神人之生。异乎众也久矣。虹流电绕之祥勿论。玄鸟帝武。圣经所著。先儒犹或疑之。而况是乎。然而天地之气生之。张朱有定论则何必稷契之信而是之疑乎。但是时中国已为衰世。而东方始有气化。岂风气之开。自有内外先后之异欤。新罗享国远过三代。朴氏昌炽。殆遍一国。其神圣始祖之生。固异乎众。而不可以常理论也。匹夫之贤。生长之地。往往见表石。千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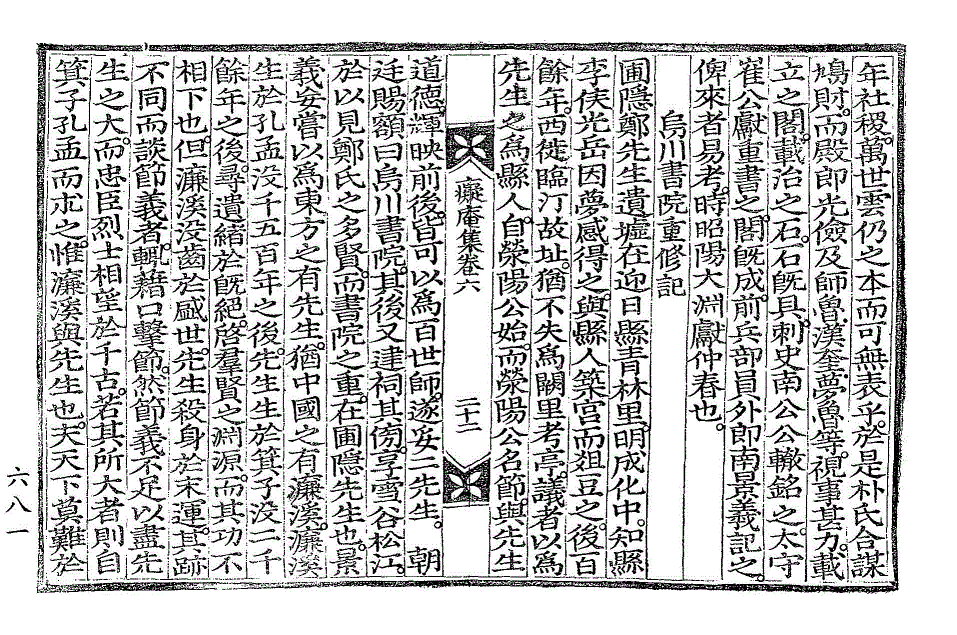 年社稷。万世云仍之本而可无表乎。于是朴氏合谋鸠财。而殿郎光俭及师鲁,汉奎,梦鲁等。视事甚力。载立之阁。载治之石。石既具。刺史南公公辙铭之。太守崔公献重书之。阁既成。前兵部员外郎南景羲记之。俾来者易考。时昭阳大渊献仲春也。
年社稷。万世云仍之本而可无表乎。于是朴氏合谋鸠财。而殿郎光俭及师鲁,汉奎,梦鲁等。视事甚力。载立之阁。载治之石。石既具。刺史南公公辙铭之。太守崔公献重书之。阁既成。前兵部员外郎南景羲记之。俾来者易考。时昭阳大渊献仲春也。乌川书院重修记
圃隐郑先生遗墟在迎日县青林里。明成化中。知县李侯光岳因梦感得之。与县人筑宫而俎豆之。后百馀年。西徙临汀故址。犹不失为阙里考亭。议者以为先生之为县人。自荥阳公始。而荥阳公名节。与先生道德。辉映前后。皆可以为百世师。遂妥二先生。 朝廷赐额曰乌川书院。其后又建祠其傍。享雪谷松江。于以见郑氏之多贤。而书院之重。在圃隐先生也。景羲妄尝以为东方之有先生。犹中国之有濂溪。濂溪生于孔孟没千五百年之后。先生生于箕子没二千馀年之后。寻遗绪于既绝。启群贤之渊源。而其功不相下也。但濂溪没齿于盛世。先生杀身于末运。其迹不同而谈节义者。辄藉口击节。然节义不足以尽先生之大。而忠臣烈士相望于千古。若其所大者则自箕子孔孟而求之。惟濂溪与先生也。夫天下莫难于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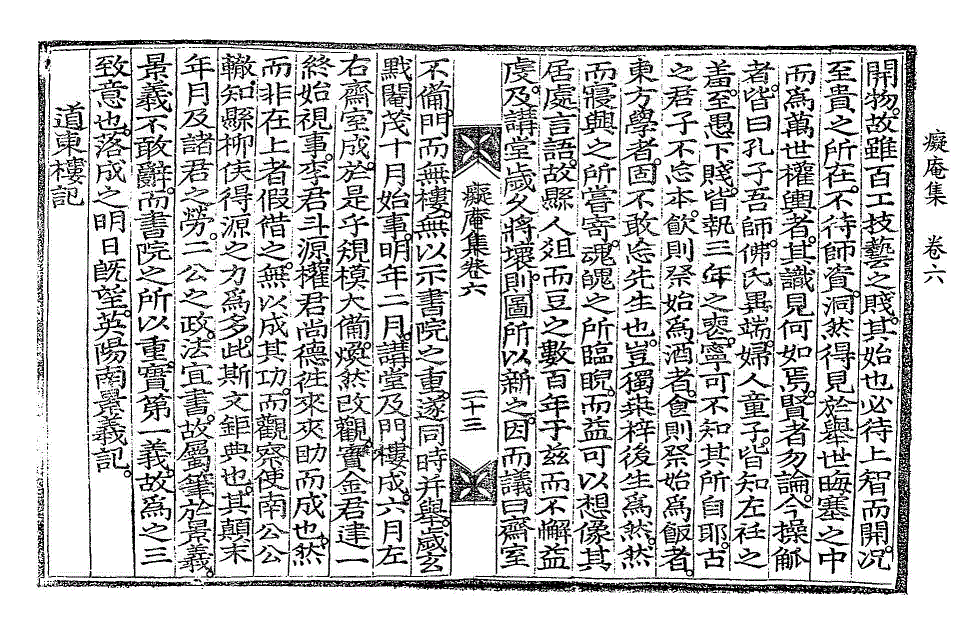 开物。故虽百工技艺之贱。其始也必待上智而开。况至贵之所在。不待师资。洞然得见于举世晦塞之中而为万世权舆者。其识见何如焉。贤者勿论。今操觚者。皆曰孔子吾师。佛氏异端。妇人童子。皆知左衽之羞。至愚下贱。皆执三年之丧。宁可不知其所自耶。古之君子不忘本。饮则祭始为酒者。食则祭始为饭者。东方学者。固不敢忘先生也。岂独桑梓后生为然。然而寝兴之所尝寄。魂魄之所临睨。而益可以想像其居处言语。故县人俎而豆之数百年于玆而不懈益虔。及讲堂岁久将坏。则图所以新之。因而议曰斋室不备。门而无楼。无以示书院之重。遂同时并举。岁玄黓阉茂十月始事。明年二月。讲堂及门楼成。六月左右斋室成。于是乎规模大备。焕然改观。实金君建一终始视事。李君斗源,权君尚德往来夹助而成也。然而非在上者假借之。无以成其功。而观察使南公公辙,知县柳侯得源之力为多。此斯文钜典也。其颠末年月及诸君之劳。二公之政。法宜书。故属笔于景羲。景羲不敢辞。而书院之所以重。实第一义。故为之三致意也。落成之明日既望。英阳南景羲记。
开物。故虽百工技艺之贱。其始也必待上智而开。况至贵之所在。不待师资。洞然得见于举世晦塞之中而为万世权舆者。其识见何如焉。贤者勿论。今操觚者。皆曰孔子吾师。佛氏异端。妇人童子。皆知左衽之羞。至愚下贱。皆执三年之丧。宁可不知其所自耶。古之君子不忘本。饮则祭始为酒者。食则祭始为饭者。东方学者。固不敢忘先生也。岂独桑梓后生为然。然而寝兴之所尝寄。魂魄之所临睨。而益可以想像其居处言语。故县人俎而豆之数百年于玆而不懈益虔。及讲堂岁久将坏。则图所以新之。因而议曰斋室不备。门而无楼。无以示书院之重。遂同时并举。岁玄黓阉茂十月始事。明年二月。讲堂及门楼成。六月左右斋室成。于是乎规模大备。焕然改观。实金君建一终始视事。李君斗源,权君尚德往来夹助而成也。然而非在上者假借之。无以成其功。而观察使南公公辙,知县柳侯得源之力为多。此斯文钜典也。其颠末年月及诸君之劳。二公之政。法宜书。故属笔于景羲。景羲不敢辞。而书院之所以重。实第一义。故为之三致意也。落成之明日既望。英阳南景羲记。道东楼记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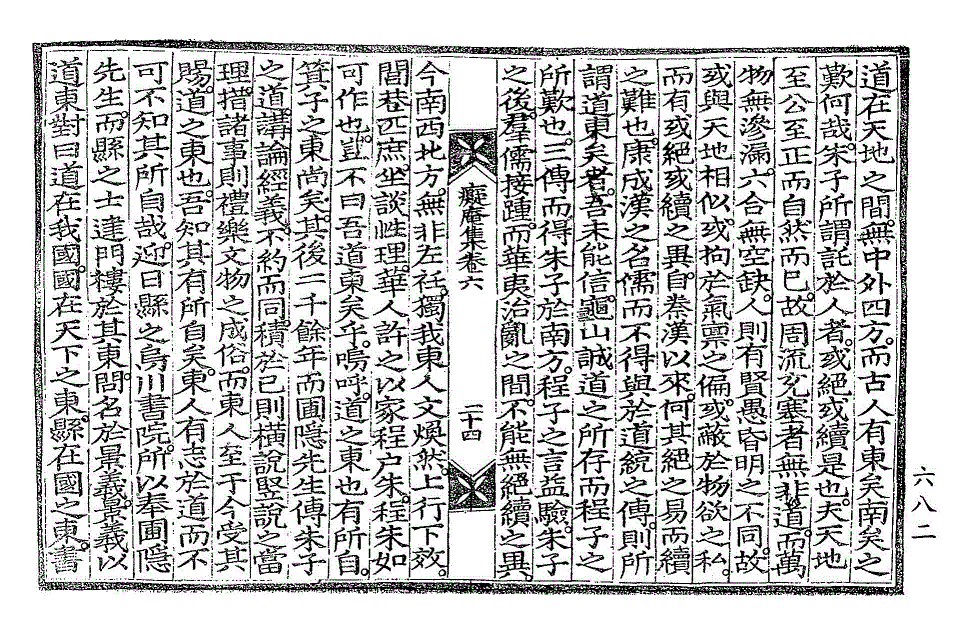 道在天地之间。无中外四方。而古人有东矣南矣之叹何哉。朱子所谓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是也。夫天地至公至正而自然而已。故周流充塞者无非道。而万物无渗漏。六合无空缺。人则有贤愚昏明之不同。故或与天地相似。或拘于气禀之偏。或蔽于物欲之私。而有或绝或续之异。自秦汉以来。何其绝之易而续之难也。康成汉之名儒而不得与于道统之传。则所谓道东矣者。吾未能信。龟山诚道之所存而程子之所叹也。三传而得朱子于南方。程子之言益验。朱子之后。群儒接踵。而华夷治乱之间。不能无绝续之异。今南西北方。无非左衽。独我东人文焕然。上行下效。闾巷匹庶。坐谈性理。华人许之以家程户朱。程朱如可作也。岂不曰吾道东矣乎。呜呼。道之东也有所自。箕子之东尚矣。其后二千馀年而圃隐先生传朱子之道。讲论经义。不约而同。积于己则横说竖说之当理。措诸事则礼乐文物之成俗。而东人至于今受其赐。道之东也。吾知其有所自矣。东人有志于道而不可不知其所自哉。迎日县之乌川书院。所以奉圃隐先生。而县之士建门楼于其东。问名于景羲。景羲以道东对曰道在我国。国在天下之东。县在国之东。书
道在天地之间。无中外四方。而古人有东矣南矣之叹何哉。朱子所谓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是也。夫天地至公至正而自然而已。故周流充塞者无非道。而万物无渗漏。六合无空缺。人则有贤愚昏明之不同。故或与天地相似。或拘于气禀之偏。或蔽于物欲之私。而有或绝或续之异。自秦汉以来。何其绝之易而续之难也。康成汉之名儒而不得与于道统之传。则所谓道东矣者。吾未能信。龟山诚道之所存而程子之所叹也。三传而得朱子于南方。程子之言益验。朱子之后。群儒接踵。而华夷治乱之间。不能无绝续之异。今南西北方。无非左衽。独我东人文焕然。上行下效。闾巷匹庶。坐谈性理。华人许之以家程户朱。程朱如可作也。岂不曰吾道东矣乎。呜呼。道之东也有所自。箕子之东尚矣。其后二千馀年而圃隐先生传朱子之道。讲论经义。不约而同。积于己则横说竖说之当理。措诸事则礼乐文物之成俗。而东人至于今受其赐。道之东也。吾知其有所自矣。东人有志于道而不可不知其所自哉。迎日县之乌川书院。所以奉圃隐先生。而县之士建门楼于其东。问名于景羲。景羲以道东对曰道在我国。国在天下之东。县在国之东。书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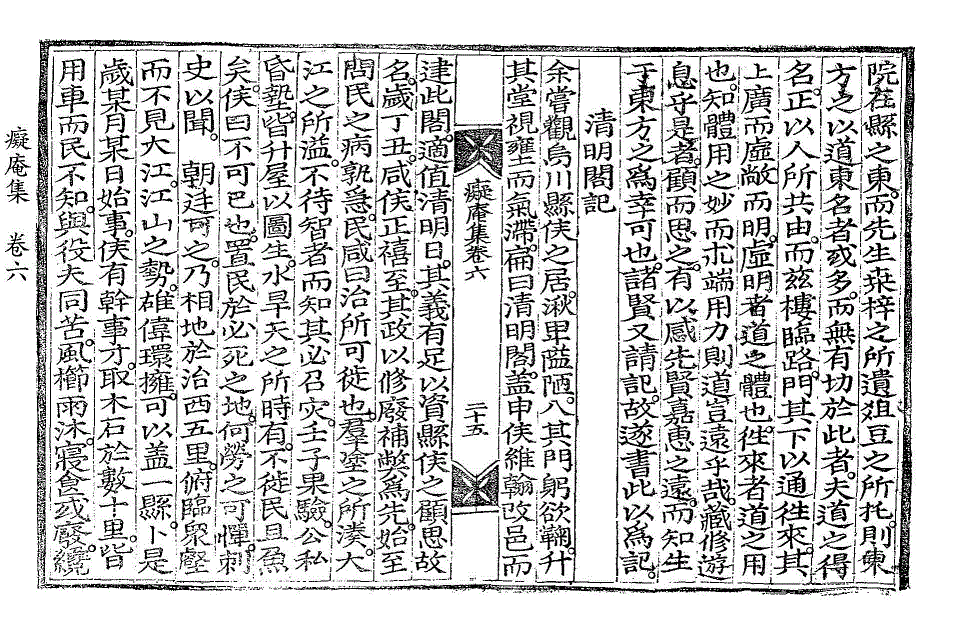 院在县之东。而先生桑梓之所遗俎豆之所托。则东方之以道东名者或多。而无有切于此者。夫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而玆楼临路。门其下以通往来。其上广而虚敞而明。虚明者道之体也。往来者道之用也。知体用之妙而求端用力则道岂远乎哉。藏修游息乎是者。顾而思之。有以感先贤嘉惠之远。而知生于东方之为幸可也。诸贤又请记。故遂书此以为记。
院在县之东。而先生桑梓之所遗俎豆之所托。则东方之以道东名者或多。而无有切于此者。夫道之得名。正以人所共由。而玆楼临路。门其下以通往来。其上广而虚敞而明。虚明者道之体也。往来者道之用也。知体用之妙而求端用力则道岂远乎哉。藏修游息乎是者。顾而思之。有以感先贤嘉惠之远。而知生于东方之为幸可也。诸贤又请记。故遂书此以为记。清明阁记
余尝观乌川县侯之居。湫卑隘陋。入其门躬欲鞠。升其堂视壅而气滞。扁曰清明阁。盖申侯维翰改邑而建此阁。适值清明日。其义有足以资县侯之顾思故名。岁丁丑。咸侯正禧至。其政以修废补弊为先。始至问民之病孰急。民咸曰治所可徙也。群涂之所凑。大江之所溢。不待智者而知其必召灾。壬子果验。公私昏垫。皆升屋以图生。水旱天之所时有。不徙民且鱼矣。侯曰不可已也。置民于必死之地。何劳之可惮。刺史以闻。 朝廷可之。乃相地于治西五里。俯临众壑而不见大江。江山之势。雄伟环拥。可以盖一县。卜是岁某月某日始事。侯有干事才。取木石于数十里。皆用车而民不知。与役夫同苦。风栉雨沐。寝食或废。才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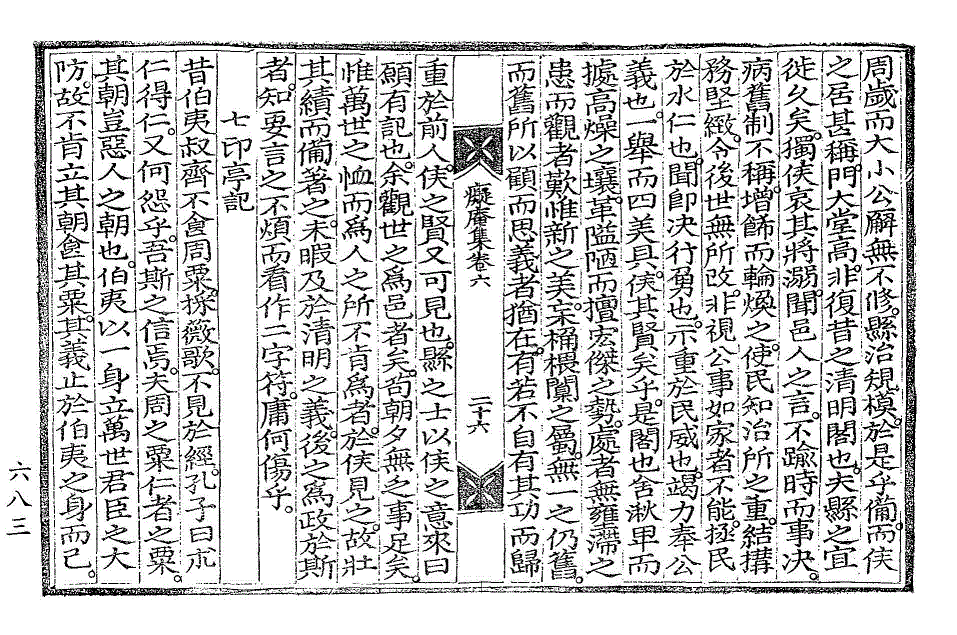 周岁而大小公廨无不修。县治规模。于是乎备。而侯之居甚称。门大堂高。非复昔之清明阁也。夫县之宜徙久矣。独侯哀其将溺。闻邑人之言。不踰时而事决。病旧制不称。增饰而轮焕之。使民知治所之重。结搆务坚致。令后世无所改。非视公事如家者不能。拯民于水仁也。闻即决行勇也。示重于民威也。竭力奉公义也。一举而四美具。侯其贤矣乎。是阁也舍湫卑而据高燥之壤。革隘陋而擅宏杰之势。处者无壅滞之患而观者叹惟新之美。杗桷椳闑之属。无一之仍旧。而旧所以顾而思义者犹在。有若不自有其功而归重于前人。侯之贤又可见也。县之士以侯之意来曰愿有记也。余观世之为邑者矣。苟朝夕无乏事足矣。惟万世之恤而为人之所不肯为者。于侯见之。故壮其绩而备著之。未暇及于清明之义。后之为政于斯者。知要言之不烦而看作二字符。庸何伤乎。
周岁而大小公廨无不修。县治规模。于是乎备。而侯之居甚称。门大堂高。非复昔之清明阁也。夫县之宜徙久矣。独侯哀其将溺。闻邑人之言。不踰时而事决。病旧制不称。增饰而轮焕之。使民知治所之重。结搆务坚致。令后世无所改。非视公事如家者不能。拯民于水仁也。闻即决行勇也。示重于民威也。竭力奉公义也。一举而四美具。侯其贤矣乎。是阁也舍湫卑而据高燥之壤。革隘陋而擅宏杰之势。处者无壅滞之患而观者叹惟新之美。杗桷椳闑之属。无一之仍旧。而旧所以顾而思义者犹在。有若不自有其功而归重于前人。侯之贤又可见也。县之士以侯之意来曰愿有记也。余观世之为邑者矣。苟朝夕无乏事足矣。惟万世之恤而为人之所不肯为者。于侯见之。故壮其绩而备著之。未暇及于清明之义。后之为政于斯者。知要言之不烦而看作二字符。庸何伤乎。七印亭记
昔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歌。不见于经。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吾斯之信焉。夫周之粟仁者之粟。其朝岂恶人之朝也。伯夷以一身立万世君臣之大防。故不肯立其朝食其粟。其义止于伯夷之身而已。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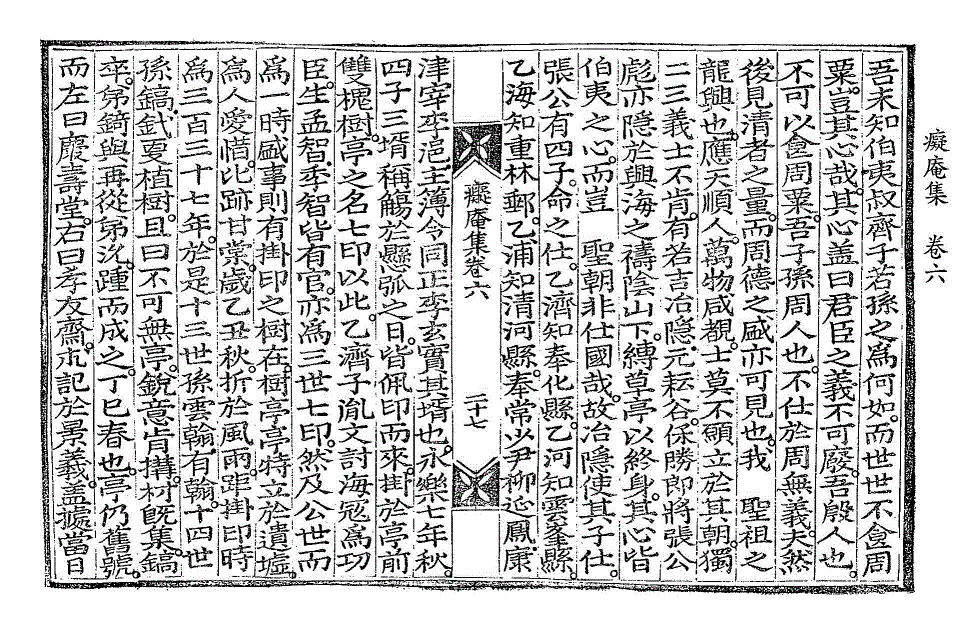 吾未知伯夷叔齐子若孙之为何如。而世世不食周粟。岂其心哉。其心盖曰君臣之义不可废。吾殷人也。不可以食周粟。吾子孙周人也。不仕于周无义。夫然后见清者之量。而周德之盛亦可见也。我 圣祖之龙兴也。应天顺人。万物咸睹。士莫不愿立于其朝。独二三义士不肯。有若吉冶隐,元耘谷。保胜郎将张公彪亦隐于兴海之祷阴山下。缚草亭以终身。其心皆伯夷之心。而岂 圣朝非仕国哉。故冶隐使其子仕。张公有四子。命之仕。乙济知奉化县。乙河知云峰县。乙海知重林邮。乙浦知清河县。奉常少尹柳延凤,康津宰李浥,主簿令同正李玄实其婿也。永乐七年秋。四子三婿称觞于悬弧之日。皆佩印而来。挂于亭前双槐树。亭之名七印以此。乙济子胤文讨海寇为功臣。生孟智,季智皆有官。亦为三世七印。然及公世而为一时盛事则有挂印之树在。树亭亭特立于遗墟。为人爱惜。比迹甘棠。岁乙丑秋。折于风雨。距挂印时为三百三十七年。于是十三世孙云翰,有翰。十四世孙镐,釴更植树。且曰不可无亭。锐意肯搆。材既集。镐卒。弟锜与再从弟沇。踵而成之。丁巳春也。亭仍旧号。而左曰庆寿堂。右曰孝友斋。求记于景羲。盖据当日
吾未知伯夷叔齐子若孙之为何如。而世世不食周粟。岂其心哉。其心盖曰君臣之义不可废。吾殷人也。不可以食周粟。吾子孙周人也。不仕于周无义。夫然后见清者之量。而周德之盛亦可见也。我 圣祖之龙兴也。应天顺人。万物咸睹。士莫不愿立于其朝。独二三义士不肯。有若吉冶隐,元耘谷。保胜郎将张公彪亦隐于兴海之祷阴山下。缚草亭以终身。其心皆伯夷之心。而岂 圣朝非仕国哉。故冶隐使其子仕。张公有四子。命之仕。乙济知奉化县。乙河知云峰县。乙海知重林邮。乙浦知清河县。奉常少尹柳延凤,康津宰李浥,主簿令同正李玄实其婿也。永乐七年秋。四子三婿称觞于悬弧之日。皆佩印而来。挂于亭前双槐树。亭之名七印以此。乙济子胤文讨海寇为功臣。生孟智,季智皆有官。亦为三世七印。然及公世而为一时盛事则有挂印之树在。树亭亭特立于遗墟。为人爱惜。比迹甘棠。岁乙丑秋。折于风雨。距挂印时为三百三十七年。于是十三世孙云翰,有翰。十四世孙镐,釴更植树。且曰不可无亭。锐意肯搆。材既集。镐卒。弟锜与再从弟沇。踵而成之。丁巳春也。亭仍旧号。而左曰庆寿堂。右曰孝友斋。求记于景羲。盖据当日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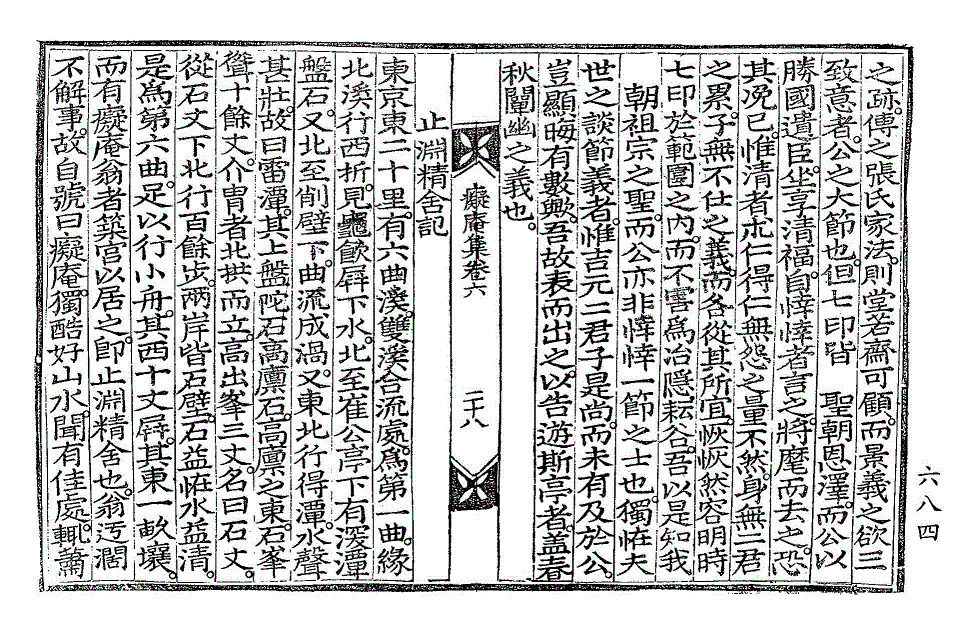 之迹。传之张氏家法。则堂若斋可顾。而景羲之欲三致意者。公之大节也。但七印皆 圣朝恩泽。而公以胜国遗臣。坐享清福。自悻悻者言之。将麾而去之。恐其浼己。惟清者求仁得仁无怨之量不然。身无二君之累。子无不仕之义。而各从其所宜。恢恢然容明时七印于范围之内。而不害为冶隐,耘谷。吾以是知我 朝祖宗之圣。而公亦非悻悻一节之士也。独怪夫世之谈节义者。惟吉元二君子是尚。而未有及于公。岂显晦有数欤。吾故表而出之。以告游斯亭者。盖春秋阐幽之义也。
之迹。传之张氏家法。则堂若斋可顾。而景羲之欲三致意者。公之大节也。但七印皆 圣朝恩泽。而公以胜国遗臣。坐享清福。自悻悻者言之。将麾而去之。恐其浼己。惟清者求仁得仁无怨之量不然。身无二君之累。子无不仕之义。而各从其所宜。恢恢然容明时七印于范围之内。而不害为冶隐,耘谷。吾以是知我 朝祖宗之圣。而公亦非悻悻一节之士也。独怪夫世之谈节义者。惟吉元二君子是尚。而未有及于公。岂显晦有数欤。吾故表而出之。以告游斯亭者。盖春秋阐幽之义也。止渊精舍记
东京东二十里。有六曲溪。双溪合流处。为第一曲。缘北溪行西折。见龟饮屏下水。北至崔公亭下有深潭盘石。又北至削壁下。曲流成涡。又东北行得潭。水声甚壮。故曰雷潭。其上盘陀石高廪石。高廪之东。石峰耸十馀丈。介冑者北拱而立。高出峰三丈。名曰石丈。从石丈下北行百馀步。两岸皆石壁。石益怪水益清。是为第六曲。足以行小舟。其西十丈屏。其东一亩壤。而有痴庵翁者筑宫以居之。即止渊精舍也。翁迂阔不解事。故自号曰痴庵。独酷好山水。闻有佳处。辄萧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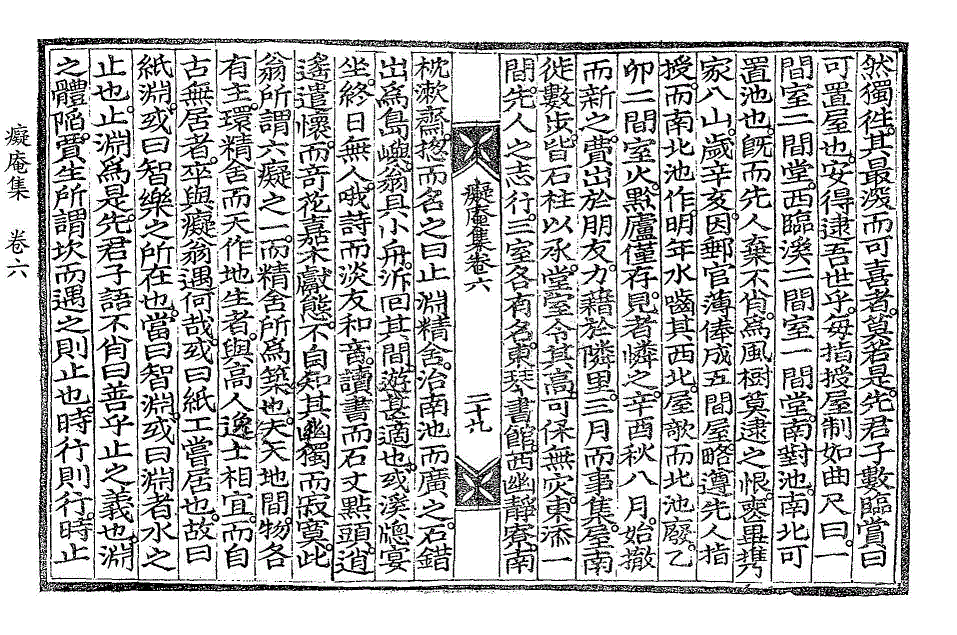 然独往。其最深而可喜者。莫若是。先君子数临赏曰可置屋也。安得逮吾世乎。每指授屋制如曲尺曰。一间室二间堂。西临溪二间室一间堂。南对池。南北可置池也。既而先人弃不肖。为风树莫逮之恨。丧毕携家入山。岁辛亥。因邮官薄俸成五间屋。略遵先人指授。而南北池作。明年水啮其西北。屋欹而北池废。乙卯二间室火。黔庐仅存。见者怜之。辛酉秋八月。始撤而新之。费出于朋友。力藉于邻里。三月而事集。屋南徙数步。皆石柱以承。堂室令其高。可保无灾。东添一间。先人之志行。三室各有名。东琴书馆。西幽静寮。南枕漱斋。揔而名之曰止渊精舍。治南池而广之。石错出为岛屿。翁具小舟。溯回其间。游甚适也。或溪窗宴坐。终日无人。哦诗而淡友和音。读书而石丈点头。逍遥遣怀。而奇花嘉木献态。不自知其幽独而寂寞。此翁所谓六痴之一。而精舍所为筑也。夫天地间。物各有主。环精舍而天作地生者。与高人逸士相宜。而自古无居者。卒与痴翁遇何哉。或曰纸工尝居也。故曰纸渊。或曰智乐之所在也。当曰智渊。或曰渊者水之止也。止渊为是。先君子语不肖曰善乎止之义也。渊之体陷。贾生所谓坎而遇之则止也。时行则行。时止
然独往。其最深而可喜者。莫若是。先君子数临赏曰可置屋也。安得逮吾世乎。每指授屋制如曲尺曰。一间室二间堂。西临溪二间室一间堂。南对池。南北可置池也。既而先人弃不肖。为风树莫逮之恨。丧毕携家入山。岁辛亥。因邮官薄俸成五间屋。略遵先人指授。而南北池作。明年水啮其西北。屋欹而北池废。乙卯二间室火。黔庐仅存。见者怜之。辛酉秋八月。始撤而新之。费出于朋友。力藉于邻里。三月而事集。屋南徙数步。皆石柱以承。堂室令其高。可保无灾。东添一间。先人之志行。三室各有名。东琴书馆。西幽静寮。南枕漱斋。揔而名之曰止渊精舍。治南池而广之。石错出为岛屿。翁具小舟。溯回其间。游甚适也。或溪窗宴坐。终日无人。哦诗而淡友和音。读书而石丈点头。逍遥遣怀。而奇花嘉木献态。不自知其幽独而寂寞。此翁所谓六痴之一。而精舍所为筑也。夫天地间。物各有主。环精舍而天作地生者。与高人逸士相宜。而自古无居者。卒与痴翁遇何哉。或曰纸工尝居也。故曰纸渊。或曰智乐之所在也。当曰智渊。或曰渊者水之止也。止渊为是。先君子语不肖曰善乎止之义也。渊之体陷。贾生所谓坎而遇之则止也。时行则行。时止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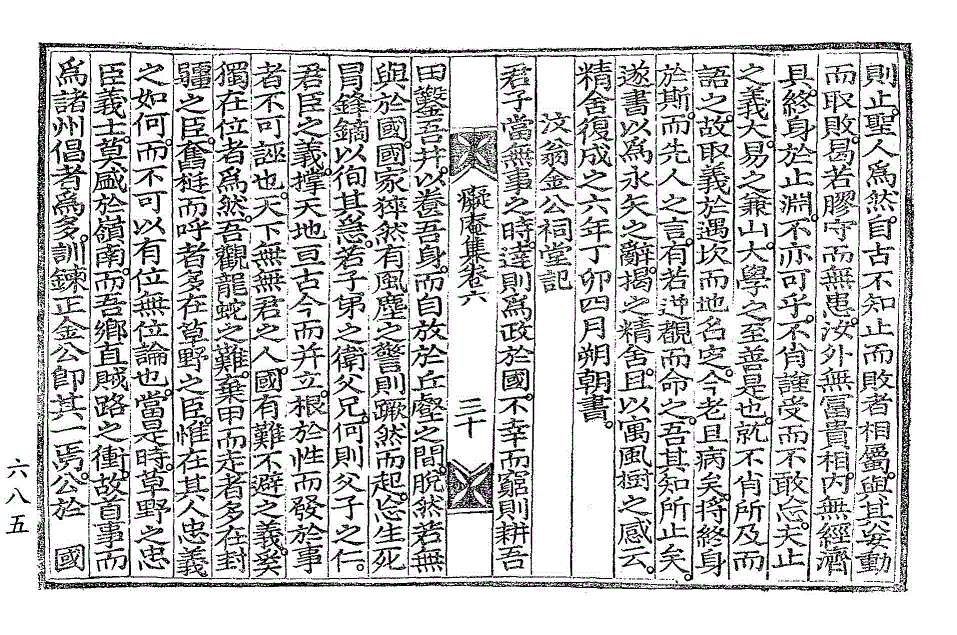 则止。圣人为然。自古不知止而败者相属。与其妄动而取败。曷若胶守而无患。汝外无富贵相。内无经济具。终身于止渊。不亦可乎。不肖谨受而不敢忘。夫止之义大。易之兼山。大学之至善是也。就不肖所及而语之。故取义于遇坎而地名定。今老且病矣。将终身于斯。而先人之言。有若逆睹而命之。吾其知所止矣。遂书以为永矢之辞。揭之精舍。且以寓风树之感云。精舍复成之六年丁卯四月朔朝书。
则止。圣人为然。自古不知止而败者相属。与其妄动而取败。曷若胶守而无患。汝外无富贵相。内无经济具。终身于止渊。不亦可乎。不肖谨受而不敢忘。夫止之义大。易之兼山。大学之至善是也。就不肖所及而语之。故取义于遇坎而地名定。今老且病矣。将终身于斯。而先人之言。有若逆睹而命之。吾其知所止矣。遂书以为永矢之辞。揭之精舍。且以寓风树之感云。精舍复成之六年丁卯四月朔朝书。汶翁金公祠堂记
君子当无事之时。达则为政于国。不幸而穷则耕吾田凿吾井。以养吾身。而自放于丘壑之间。脱然若无与于国。国家猝然有风尘之警则蹶然而起。忘生死冒锋镝以徇其急。若子弟之卫父兄。何则父子之仁。君臣之义。撑天地亘古今而并立。根于性而发于事者不可诬也。天下无无君之人。国有难不避之义。奚独在位者为然。吾观龙蛇之难。弃甲而走者多在封疆之臣。奋梃而呼者多在草野之臣。惟在其人忠义之如何。而不可以有位无位论也。当是时。草野之忠臣义士。莫盛于岭南。而吾乡直贼路之冲。故首事而为诸州倡者为多。训鍊正金公即其一焉。公于 国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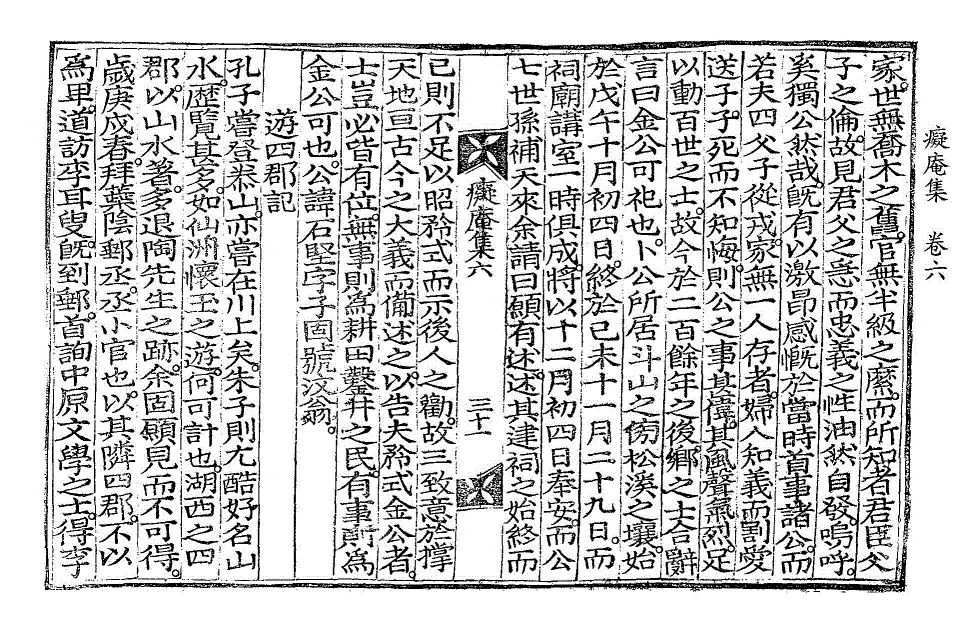 家。世无乔木之旧。官无半级之縻。而所知者君臣父子之伦。故见君父之急而忠义之性油然自发。呜呼。奚独公然哉。既有以激昂感慨于当时首事诸公。而若夫四父子从戎。家无一人存者。妇人知义而割爱送子。子死而不知悔。则公之事甚伟。其风声气烈。足以动百世之士。故今于二百馀年之后。乡之士合辞言曰金公可祀也。卜公所居斗山之傍松溪之壤。始于戊午十月初四日。终于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而祠庙讲室一时俱成。将以十二月初四日奉安。而公七世孙补天来余请曰愿有述。述其建祠之始终而已则不足以昭矜式而示后人之劝。故三致意于撑天地亘古今之大义而备述之。以告夫矜式金公者。士岂必皆有位。无事则为耕田凿井之民。有事则为金公可也。公讳石坚字子固号汶翁。
家。世无乔木之旧。官无半级之縻。而所知者君臣父子之伦。故见君父之急而忠义之性油然自发。呜呼。奚独公然哉。既有以激昂感慨于当时首事诸公。而若夫四父子从戎。家无一人存者。妇人知义而割爱送子。子死而不知悔。则公之事甚伟。其风声气烈。足以动百世之士。故今于二百馀年之后。乡之士合辞言曰金公可祀也。卜公所居斗山之傍松溪之壤。始于戊午十月初四日。终于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而祠庙讲室一时俱成。将以十二月初四日奉安。而公七世孙补天来余请曰愿有述。述其建祠之始终而已则不足以昭矜式而示后人之劝。故三致意于撑天地亘古今之大义而备述之。以告夫矜式金公者。士岂必皆有位。无事则为耕田凿井之民。有事则为金公可也。公讳石坚字子固号汶翁。游四郡记
孔子尝登泰山。亦尝在川上矣。朱子则尤酷好名山水。历览甚多。如仙洲怀玉之游。何可计也。湖西之四郡。以山水著。多退陶先生之迹。余固愿见而不可得。岁庚戌春。拜蕊阴邮丞。丞小官也。以其邻四郡。不以为卑。道访李耳叟。既到邮。首询中原文学之士。得李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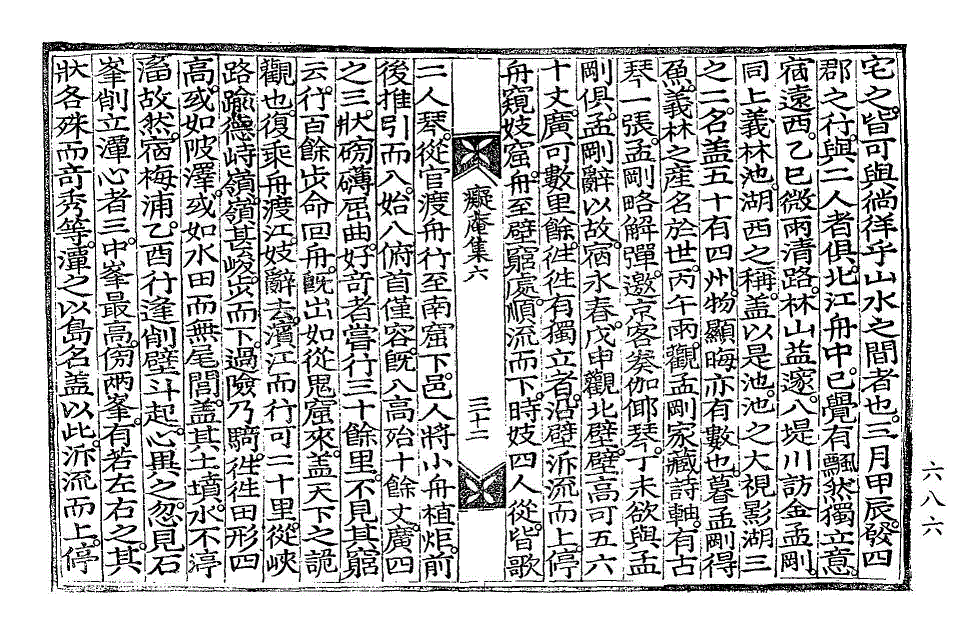 宅之。皆可与徜徉乎山水之间者也。三月甲辰。发四郡之行。与二人者俱。北江舟中。已觉有飘然独立意。宿远西。乙巳微雨清路。林山益邃。入堤川访金孟刚。同上义林池。湖西之称。盖以是池。池之大视影湖三之二。名盖五十有四州。物显晦亦有数也。暮孟刚得鱼。义林之产名于世。丙午雨。观孟刚家藏诗轴。有古琴一张。孟刚略解弹。邀京客奏伽倻琴。丁未欲与孟刚俱。孟刚辞以故。宿永春。戊申观北壁。壁高可五六十丈。广可数里馀。往往有独立者。沿壁溯流而上。停舟窥妓窟。舟至壁穷处。顺流而下。时妓四人从。皆歌二人琴。从官渡舟行至南窟下。邑人将小舟植炬。前后推引而入。始入俯首仅容。既入高殆十馀丈。广四之三。状磅礴屈曲。好奇者尝行三十馀里。不见其穷云。行百馀步命回舟。既出如从鬼窟来。盖天下之诡观也。复乘舟渡江。妓辞去。滨江而行可二十里。从峡路踰德峙岭。岭甚峻。步而下。过险乃骑。往往田形四高。或如陂泽。或如水田而无尾闾。盖其土坟。水不渟滀故然。宿梅浦。乙酉行逢削壁斗起。心异之。忽见石峰削立潭心者三。中峰最高。傍两峰。有若左右之。其状各殊而奇秀等。潭之以岛名盖以此。溯流而上。停
宅之。皆可与徜徉乎山水之间者也。三月甲辰。发四郡之行。与二人者俱。北江舟中。已觉有飘然独立意。宿远西。乙巳微雨清路。林山益邃。入堤川访金孟刚。同上义林池。湖西之称。盖以是池。池之大视影湖三之二。名盖五十有四州。物显晦亦有数也。暮孟刚得鱼。义林之产名于世。丙午雨。观孟刚家藏诗轴。有古琴一张。孟刚略解弹。邀京客奏伽倻琴。丁未欲与孟刚俱。孟刚辞以故。宿永春。戊申观北壁。壁高可五六十丈。广可数里馀。往往有独立者。沿壁溯流而上。停舟窥妓窟。舟至壁穷处。顺流而下。时妓四人从。皆歌二人琴。从官渡舟行至南窟下。邑人将小舟植炬。前后推引而入。始入俯首仅容。既入高殆十馀丈。广四之三。状磅礴屈曲。好奇者尝行三十馀里。不见其穷云。行百馀步命回舟。既出如从鬼窟来。盖天下之诡观也。复乘舟渡江。妓辞去。滨江而行可二十里。从峡路踰德峙岭。岭甚峻。步而下。过险乃骑。往往田形四高。或如陂泽。或如水田而无尾闾。盖其土坟。水不渟滀故然。宿梅浦。乙酉行逢削壁斗起。心异之。忽见石峰削立潭心者三。中峰最高。傍两峰。有若左右之。其状各殊而奇秀等。潭之以岛名盖以此。溯流而上。停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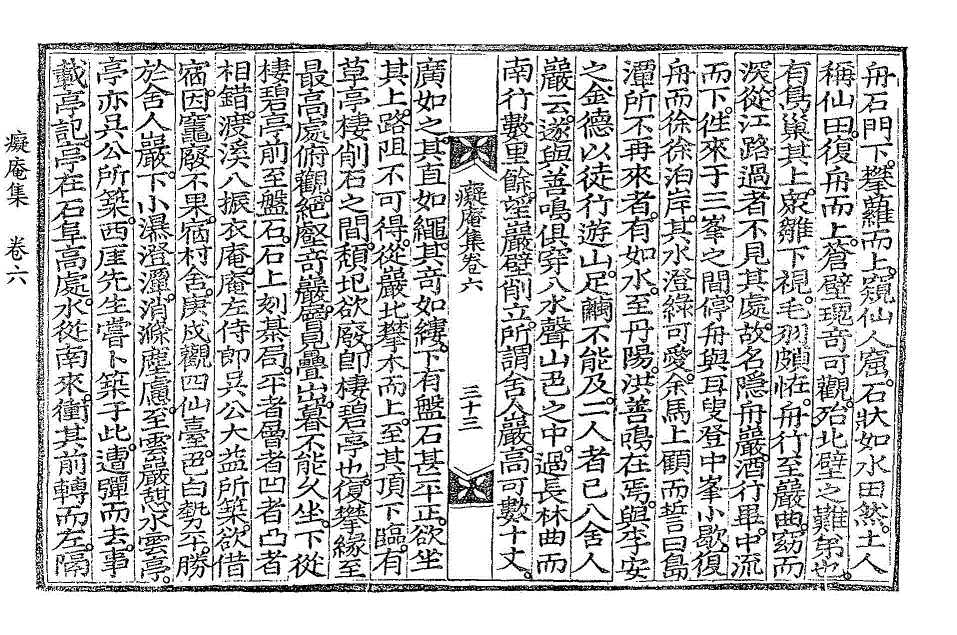 舟石门下。攀萝而上。窥仙人窟。石状如水田然。土人称仙田。复舟而上。苍壁瑰奇可观。殆北壁之难弟也。有鸟巢其上。众雏下视。毛羽颇怪。舟行至岩曲。窈而深。从江路过者不见其处。故名隐舟岩。酒行毕。中流而下。往来于三峰之间。停舟与耳叟登中峰小歇。复舟而徐徐泊岸。其水澄绿可爱。余马上顾而誓曰岛潭所不再来者。有如水。至丹阳。洪善鸣在焉。与李安之,金德以徒行游山。足茧不能及。二人者已入舍人岩云。遂与善鸣俱穿入水声山色之中。过长林曲而南行数里馀。望岩壁削立。所谓舍人岩。高可数十丈。广如之。其直如绳。其奇如缕。下有盘石甚平正。欲坐其上。路阻不可得。从岩北攀木而上。至其顶下临。有草亭栖削石之间。颓圮欲废。即栖碧亭也。复攀缘至最高处俯观。绝壑奇岩。层见叠出。暮不能久坐。下从栖碧亭前至盘石。石上刻棋局。平者层者凹者凸者相错。渡溪入振衣庵。庵左侍郎吴公大益所筑。欲借宿。因灶废不果。宿村舍。庚戌观四仙台。色白势平。胜于舍人岩。下小瀑澄潭。消涤尘虑。至云岩憩水云亭。亭亦吴公所筑。西厓先生尝卜筑于此。遭弹而去。事载亭记。亭在石阜高处。水从南来。冲其前转而左。隔
舟石门下。攀萝而上。窥仙人窟。石状如水田然。土人称仙田。复舟而上。苍壁瑰奇可观。殆北壁之难弟也。有鸟巢其上。众雏下视。毛羽颇怪。舟行至岩曲。窈而深。从江路过者不见其处。故名隐舟岩。酒行毕。中流而下。往来于三峰之间。停舟与耳叟登中峰小歇。复舟而徐徐泊岸。其水澄绿可爱。余马上顾而誓曰岛潭所不再来者。有如水。至丹阳。洪善鸣在焉。与李安之,金德以徒行游山。足茧不能及。二人者已入舍人岩云。遂与善鸣俱穿入水声山色之中。过长林曲而南行数里馀。望岩壁削立。所谓舍人岩。高可数十丈。广如之。其直如绳。其奇如缕。下有盘石甚平正。欲坐其上。路阻不可得。从岩北攀木而上。至其顶下临。有草亭栖削石之间。颓圮欲废。即栖碧亭也。复攀缘至最高处俯观。绝壑奇岩。层见叠出。暮不能久坐。下从栖碧亭前至盘石。石上刻棋局。平者层者凹者凸者相错。渡溪入振衣庵。庵左侍郎吴公大益所筑。欲借宿。因灶废不果。宿村舍。庚戌观四仙台。色白势平。胜于舍人岩。下小瀑澄潭。消涤尘虑。至云岩憩水云亭。亭亦吴公所筑。西厓先生尝卜筑于此。遭弹而去。事载亭记。亭在石阜高处。水从南来。冲其前转而左。隔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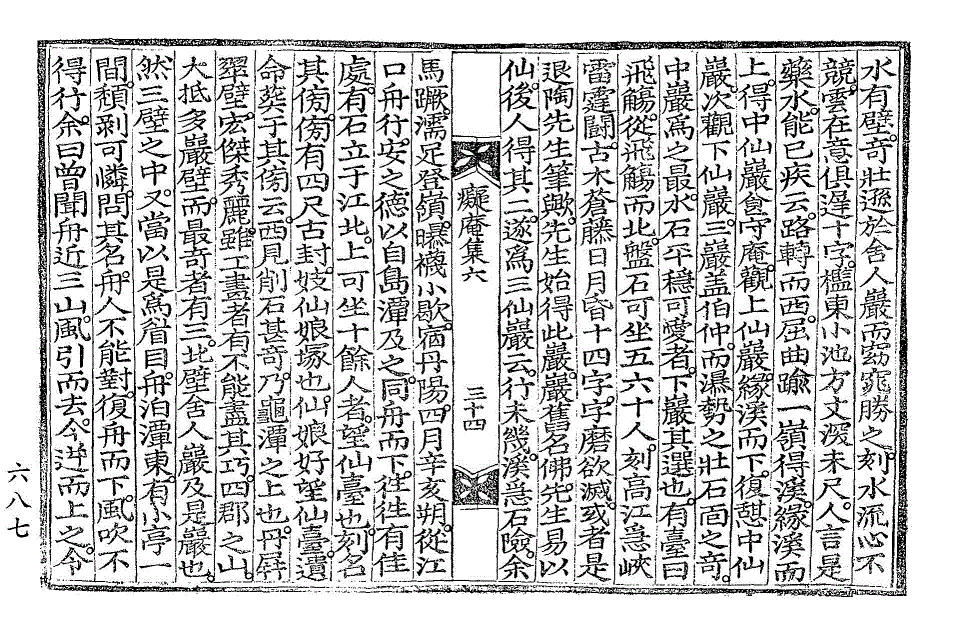 水有壁。奇壮逊于舍人岩而窈窕胜之。刻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十字。槛东小池方丈深未尺。人言是药水。能已疾云。路转而西。屈曲踰一岭得溪。缘溪而上。得中仙岩食守庵。观上仙岩。缘溪而下。复憩中仙岩。次观下仙岩。三岩盖伯仲。而瀑势之壮石面之奇。中岩为之最。水石平稳可爱者。下岩其选也。有台曰飞觞。从飞觞而北。盘石可坐五六十人。刻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十四字。字磨欲灭。或者是退陶先生笔欤。先生始得此岩。岩旧名佛。先生易以仙。后人得其二。遂为三仙岩云。行未几。溪急石险。余马蹶。濡足登岭。曝袜小歇。宿丹阳。四月辛亥朔。从江口舟行。安之,德以自岛潭及之。同舟而下。往往有佳处。有石立于江北。上可坐十馀人者。望仙台也。刻名其傍。傍有四尺古封。妓仙娘冢也。仙娘好望仙台。遗命葬于其傍云。西见削石甚奇。乃龟潭之上也。丹屏翠壁。宏杰秀丽。虽工画者有不能尽其巧。四郡之山。大抵多岩壁。而最奇者有三。北壁舍人岩及是岩也。然三壁之中。又当以是为眉目。舟泊潭东。有小亭一间。颓剥可怜。问其名。舟人不能对。复舟而下。风吹不得行。余曰曾闻舟近三山。风引而去。今逆而上之。令
水有壁。奇壮逊于舍人岩而窈窕胜之。刻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十字。槛东小池方丈深未尺。人言是药水。能已疾云。路转而西。屈曲踰一岭得溪。缘溪而上。得中仙岩食守庵。观上仙岩。缘溪而下。复憩中仙岩。次观下仙岩。三岩盖伯仲。而瀑势之壮石面之奇。中岩为之最。水石平稳可爱者。下岩其选也。有台曰飞觞。从飞觞而北。盘石可坐五六十人。刻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十四字。字磨欲灭。或者是退陶先生笔欤。先生始得此岩。岩旧名佛。先生易以仙。后人得其二。遂为三仙岩云。行未几。溪急石险。余马蹶。濡足登岭。曝袜小歇。宿丹阳。四月辛亥朔。从江口舟行。安之,德以自岛潭及之。同舟而下。往往有佳处。有石立于江北。上可坐十馀人者。望仙台也。刻名其傍。傍有四尺古封。妓仙娘冢也。仙娘好望仙台。遗命葬于其傍云。西见削石甚奇。乃龟潭之上也。丹屏翠壁。宏杰秀丽。虽工画者有不能尽其巧。四郡之山。大抵多岩壁。而最奇者有三。北壁舍人岩及是岩也。然三壁之中。又当以是为眉目。舟泊潭东。有小亭一间。颓剥可怜。问其名。舟人不能对。复舟而下。风吹不得行。余曰曾闻舟近三山。风引而去。今逆而上之。令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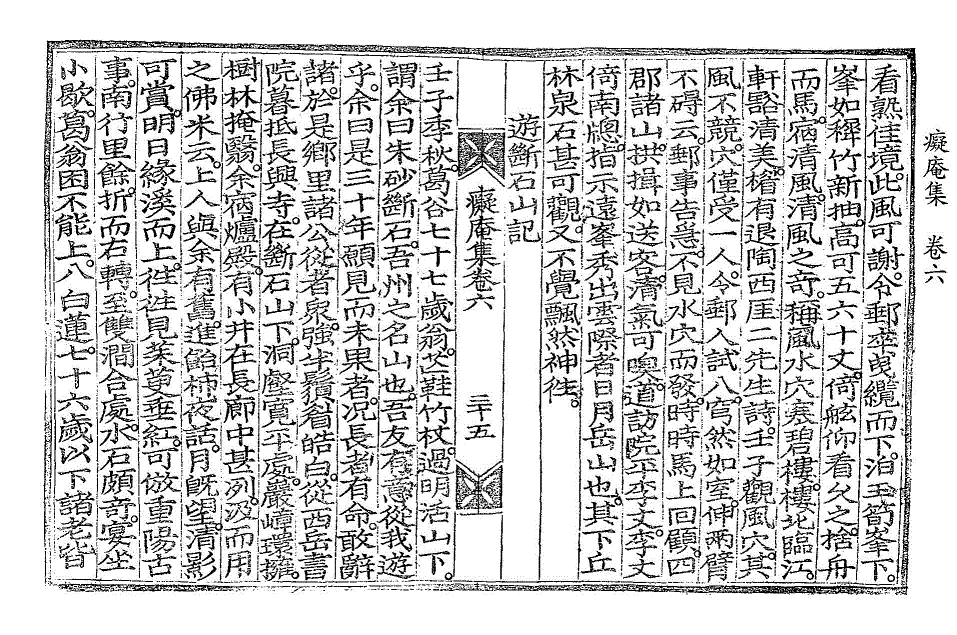 看熟佳境。此风可谢。令邮卒曳缆而下。泊玉笋峰下。峰如稚竹新抽。高可五六十丈。倚舷仰看久之。舍舟而马。宿清风。清风之奇。称风水穴寒碧楼。楼北临江。轩豁清美。楣有退陶西厓二先生诗。壬子观风穴。其风不竞。穴仅受一人。令邮人试入。穹然如室。伸两臂不碍云。邮事告急。不见水穴而发。时时马上回顾。四郡诸山。拱揖如送客。清气可嗅。道访院平李丈。李丈倚南窗。指示远峰秀出云际者曰月岳山也。其下丘林泉石甚可观。又不觉飘然神往。
看熟佳境。此风可谢。令邮卒曳缆而下。泊玉笋峰下。峰如稚竹新抽。高可五六十丈。倚舷仰看久之。舍舟而马。宿清风。清风之奇。称风水穴寒碧楼。楼北临江。轩豁清美。楣有退陶西厓二先生诗。壬子观风穴。其风不竞。穴仅受一人。令邮人试入。穹然如室。伸两臂不碍云。邮事告急。不见水穴而发。时时马上回顾。四郡诸山。拱揖如送客。清气可嗅。道访院平李丈。李丈倚南窗。指示远峰秀出云际者曰月岳山也。其下丘林泉石甚可观。又不觉飘然神往。游断石山记
壬子季秋。葛谷七十七岁翁。芒鞋竹杖。过明活山下。谓余曰朱砂断石。吾州之名山也。吾友有意从我游乎。余曰是三十年愿见而未果者。况长者有命。敢辞诸。于是乡里诸公从者众。强半须眉皓白。从西岳书院暮抵长兴寺。在断石山下。洞壑宽平处。岩嶂环拥。树林掩翳。余宿炉殿。有小井在长廊中甚冽。汲而用之佛米云。上人与余有旧。进饴柿夜话。月既望。清影可赏。明日缘溪而上。往往见茱萸垂红。可仿重阳古事。南行里馀。折而右转。至双涧合处。水石颇奇。宴坐小歇。葛翁困不能上。入白莲。七十六岁以下诸老皆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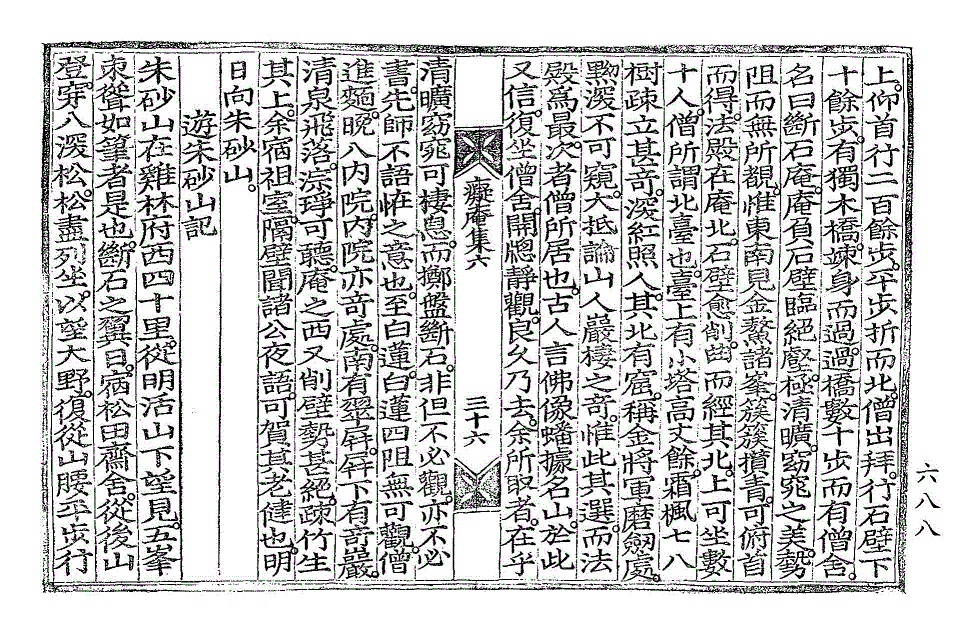 上。仰首行二百馀步。平步折而北。僧出拜。行石壁下十馀步。有独木桥。竦身而过。过桥数十步而有僧舍。名曰断石庵。庵负石壁临绝壑。极清旷。窈窕之美。势阻而无所睹。惟东南见金鳌诸峰。簇簇攒青。可俯首而得。法殿在庵北。石壁愈削。曲而经其北。上可坐数十人。僧所谓北台也。台上有小塔高丈馀。霜枫七八树疏立甚奇。深红照人。其北有窟。称金将军磨剑处。黝深不可窥。大抵论山人岩栖之奇。惟此其选。而法殿为最。次者僧所居也。古人言佛像蟠据名山。于此又信。复坐僧舍。开窗静观。良久乃去。余所取者。在乎清旷窈窕可栖息。而掷盘断石。非但不必观。亦不必书。先师不语怪之意也。至白莲。白莲四阻无可观。僧进面。晚入内院。内院亦奇处。南有翠屏。屏下有奇岩。清泉飞落。淙琤可听。庵之西又削壁势甚绝。疏竹生其上。余宿祖室。隔壁闻诸公夜语。可贺其老健也。明日向朱砂山。
上。仰首行二百馀步。平步折而北。僧出拜。行石壁下十馀步。有独木桥。竦身而过。过桥数十步而有僧舍。名曰断石庵。庵负石壁临绝壑。极清旷。窈窕之美。势阻而无所睹。惟东南见金鳌诸峰。簇簇攒青。可俯首而得。法殿在庵北。石壁愈削。曲而经其北。上可坐数十人。僧所谓北台也。台上有小塔高丈馀。霜枫七八树疏立甚奇。深红照人。其北有窟。称金将军磨剑处。黝深不可窥。大抵论山人岩栖之奇。惟此其选。而法殿为最。次者僧所居也。古人言佛像蟠据名山。于此又信。复坐僧舍。开窗静观。良久乃去。余所取者。在乎清旷窈窕可栖息。而掷盘断石。非但不必观。亦不必书。先师不语怪之意也。至白莲。白莲四阻无可观。僧进面。晚入内院。内院亦奇处。南有翠屏。屏下有奇岩。清泉飞落。淙琤可听。庵之西又削壁势甚绝。疏竹生其上。余宿祖室。隔壁闻诸公夜语。可贺其老健也。明日向朱砂山。游朱砂山记
朱砂山在鸡林府西四十里。从明活山下望见。五峰束耸如笔者是也。断石之翼日。宿松田斋舍。从后山登。穿入深松。松尽列坐。以望大野。复从山腰平步行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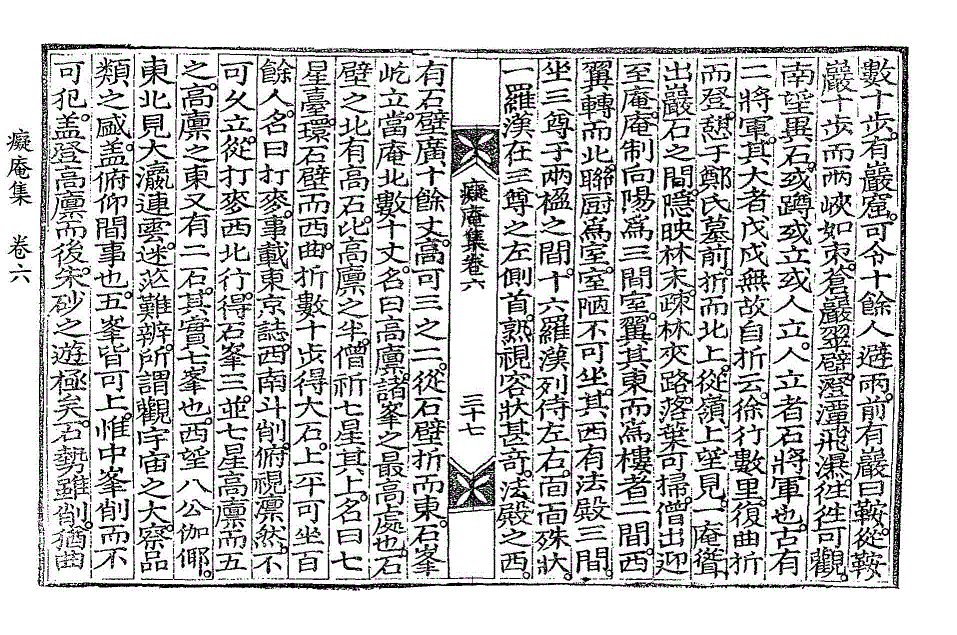 数十步。有岩窟。可令十馀人避雨。前有岩曰鞍。从鞍岩十步而两峡如束。苍岩翠壁。澄潭飞瀑。往往可观。南望异石。或蹲或立或人立。人立者石将军也。古有二将军。其大者戊戌无故自折云。徐行数里。复曲折而登。憩于郑氏墓前。折而北上。从岭上望见。一庵耸出岩石之间。隐映林末。疏林夹路。落叶可扫。僧出迎至庵。庵制向阳为三间室。翼其东而为楼者二间。西翼转而北。联厨为室。室陋不可坐。其西有法殿三间。坐三尊于两楹之间。十六罗汉列侍左右。面面殊状。一罗汉在三尊之左侧首。熟视容状甚奇。法殿之西。有石壁广十馀丈。高可三之二。从石壁折而东。石峰屹立。当庵北数十丈。名曰高廪。诸峰之最高处也。石壁之北有高石。比高廪之半。僧祈七星其上。名曰七星台。环石壁而西。曲折数十步得大石。上平可坐百馀人。名曰打麦。事载东京志。西南斗削。俯视凛然。不可久立。从打麦西北行。得石峰三。并七星高廪而五之。高廪之东又有二石。其实七峰也。西望八公伽倻。东北见大瀛连云。迷茫难辨。所谓观宇宙之大。察品类之盛。盖俯仰间事也。五峰皆可上。惟中峰削而不可犯。盖登高廪而后。朱砂之游极矣。石势虽削。犹曲
数十步。有岩窟。可令十馀人避雨。前有岩曰鞍。从鞍岩十步而两峡如束。苍岩翠壁。澄潭飞瀑。往往可观。南望异石。或蹲或立或人立。人立者石将军也。古有二将军。其大者戊戌无故自折云。徐行数里。复曲折而登。憩于郑氏墓前。折而北上。从岭上望见。一庵耸出岩石之间。隐映林末。疏林夹路。落叶可扫。僧出迎至庵。庵制向阳为三间室。翼其东而为楼者二间。西翼转而北。联厨为室。室陋不可坐。其西有法殿三间。坐三尊于两楹之间。十六罗汉列侍左右。面面殊状。一罗汉在三尊之左侧首。熟视容状甚奇。法殿之西。有石壁广十馀丈。高可三之二。从石壁折而东。石峰屹立。当庵北数十丈。名曰高廪。诸峰之最高处也。石壁之北有高石。比高廪之半。僧祈七星其上。名曰七星台。环石壁而西。曲折数十步得大石。上平可坐百馀人。名曰打麦。事载东京志。西南斗削。俯视凛然。不可久立。从打麦西北行。得石峰三。并七星高廪而五之。高廪之东又有二石。其实七峰也。西望八公伽倻。东北见大瀛连云。迷茫难辨。所谓观宇宙之大。察品类之盛。盖俯仰间事也。五峰皆可上。惟中峰削而不可犯。盖登高廪而后。朱砂之游极矣。石势虽削。犹曲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89L 页
 折成阶。可受一足。余衣冠不变。持杖徐徐而上。知顶上不属朱砂。验道体之无穷然后。飘然而下。盖同游诸公之所未能也。日将夕矣。庵僧告饭具。饭后联袂而下。下数十步。列坐石上。方行酒。李子衡至。盖约而后焉。余与郑晦而,从子衡复上。遍观乃下。可里馀及诸公至松尽处。松田少年持酒来待。列坐以次传杯。犯黑投斋舍。不能容客。客比断石之游三倍有馀。夫朱砂名胜。诸公盛会。皆可记也。况以七十七岁翁为之首。而视绝顶如平地。观者惊叹。称神仙中人。岂不尤奇也哉。是为记。
折成阶。可受一足。余衣冠不变。持杖徐徐而上。知顶上不属朱砂。验道体之无穷然后。飘然而下。盖同游诸公之所未能也。日将夕矣。庵僧告饭具。饭后联袂而下。下数十步。列坐石上。方行酒。李子衡至。盖约而后焉。余与郑晦而,从子衡复上。遍观乃下。可里馀及诸公至松尽处。松田少年持酒来待。列坐以次传杯。犯黑投斋舍。不能容客。客比断石之游三倍有馀。夫朱砂名胜。诸公盛会。皆可记也。况以七十七岁翁为之首。而视绝顶如平地。观者惊叹。称神仙中人。岂不尤奇也哉。是为记。游大贤洞记
大贤洞古称时多佛洞。人嫌其俚。易以今名。枕流亭下水所从出也。朱砂之明日。葛翁及诸公径归。余与二三长老。寻西南峡。先观枕流亭。亭虽废。水石名于世。丁酉孟秋。尝过。今年经大水。不见深潭。石屿清瘦益奇。明日缘溪东行五里馀。折而南。复五里而至芦溪。问朴处士遗墟。野人指溪东谷口。攀木披棘而上。得废砌破瓦。地可容小屋数间。石壁环拥。微泉㶁㶁流其侧。静憩有顷乃下。东南行七八里。有双岩水石。即大贤洞口也。盘石平铺。乍高乍低。而水曲折流其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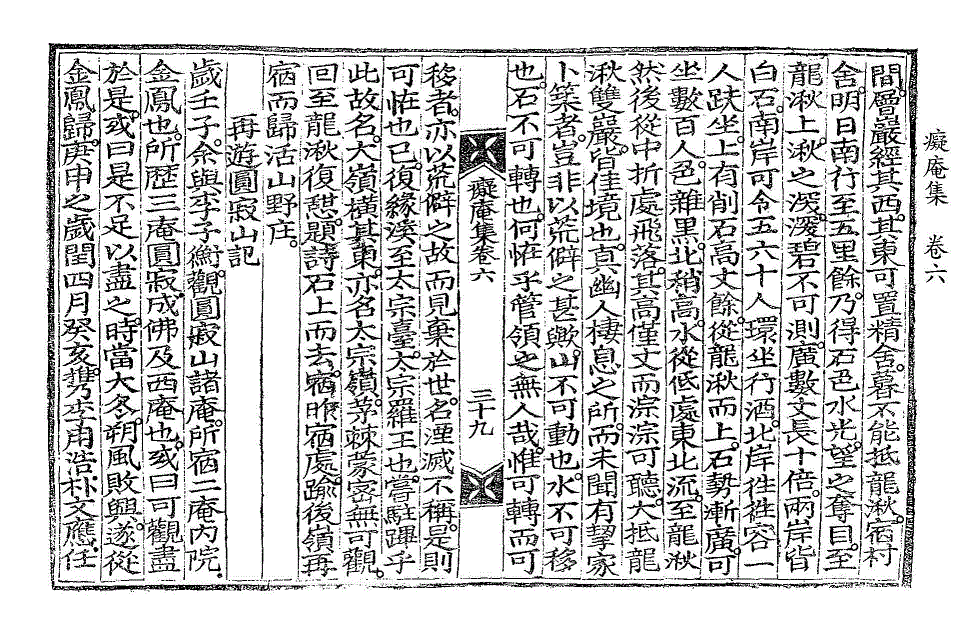 间。层岩经其西。其东可置精舍。暮不能抵龙湫。宿村舍。明日南行至五里馀。乃得石色水光。望之夺目。至龙湫上。湫之深。深碧不可测。广数丈长十倍。两岸皆白石。南岸可令五六十人环坐行酒。北岸往往容一人趺坐。上有削石高丈馀。从龙湫而上。石势渐广。可坐数百人。色杂黑。北稍高。水从低处东北流。至龙湫然后从中折处飞落。其高仅丈而淙淙可听。大抵龙湫双岩。皆佳境也。真幽人栖息之所。而未闻有挈家卜筑者。岂非以荒僻之甚欤。山不可动也。水不可移也。石不可转也。何怪乎管领之无人哉。惟可转而可移者。亦以荒僻之故而见弃于世。名湮灭不称。是则可怪也已。复缘溪至太宗台。太宗罗王也。尝驻跸乎此故名。大岭横其东。亦名太宗岭。茅棘蒙密无可观。回至龙湫复憩。题诗石上而去。宿昨宿处。踰后岭再宿而归活山野庄。
间。层岩经其西。其东可置精舍。暮不能抵龙湫。宿村舍。明日南行至五里馀。乃得石色水光。望之夺目。至龙湫上。湫之深。深碧不可测。广数丈长十倍。两岸皆白石。南岸可令五六十人环坐行酒。北岸往往容一人趺坐。上有削石高丈馀。从龙湫而上。石势渐广。可坐数百人。色杂黑。北稍高。水从低处东北流。至龙湫然后从中折处飞落。其高仅丈而淙淙可听。大抵龙湫双岩。皆佳境也。真幽人栖息之所。而未闻有挈家卜筑者。岂非以荒僻之甚欤。山不可动也。水不可移也。石不可转也。何怪乎管领之无人哉。惟可转而可移者。亦以荒僻之故而见弃于世。名湮灭不称。是则可怪也已。复缘溪至太宗台。太宗罗王也。尝驻跸乎此故名。大岭横其东。亦名太宗岭。茅棘蒙密无可观。回至龙湫复憩。题诗石上而去。宿昨宿处。踰后岭再宿而归活山野庄。再游圆寂山记
岁壬子。余与李子衡。观圆寂山诸庵。所宿二庵内院,金凤也。所历三庵圆寂,成佛及西庵也。或曰可观尽于是。或曰是不足以尽之。时当大冬。朔风败兴。遂从金凤归。庚申之岁闰四月癸亥。携李用浩,朴文应,任
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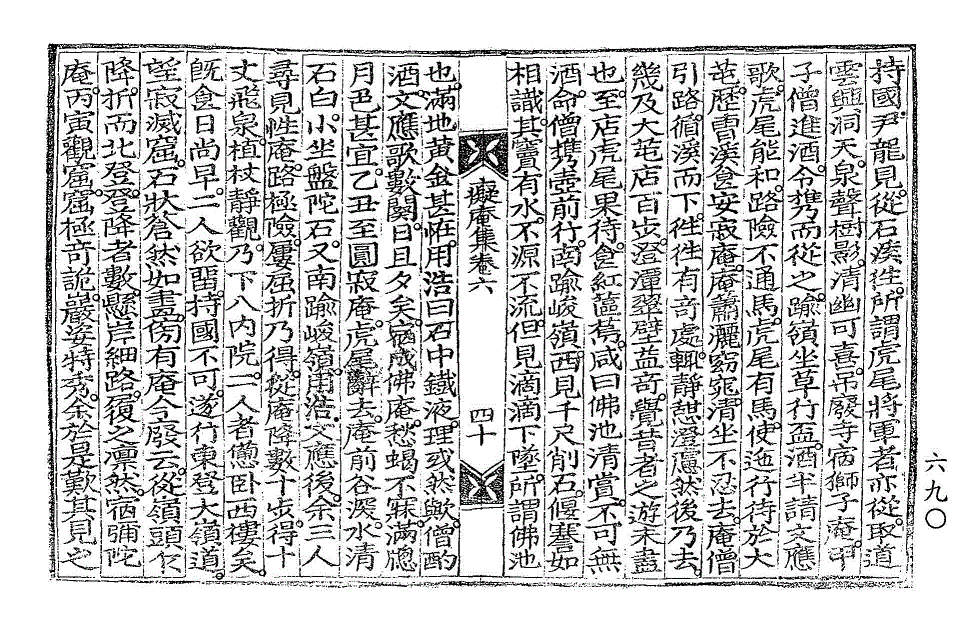 持国,尹龙见。从石溪往。所谓虎尾将军者亦从。取道云兴洞天。泉声树影。清幽可喜。吊废寺宿狮子庵。甲子僧进酒。令携而从之。踰岭坐草行杯。酒半请文应歌。虎尾能和。路险不通马。虎尾有马。使迤行待于大芚。历曹溪食安寂庵。庵萧洒窈窕。清坐不忍去。庵僧引路。循溪而下。往往有奇处。辄静憩澄虑然后乃去。几及大芚店百步。澄潭翠壁益奇。觉昔者之游未尽也。至店虎尾果待。食红蓲𦶀。咸曰佛池清赏。不可无酒。命僧携壶前行。南踰峻岭。西见千尺削石。偃謇如相识。其窦有水。不源不流。但见滴滴下坠。所谓佛池也。满地黄金甚怪。用浩曰石中铁液。理或然欤。僧酌酒。文应歌数阕。日且夕矣。宿成佛庵。愁蝎不寐。满窗月色甚宜。乙丑至圆寂庵。虎尾辞去。庵前谷深。水清石白。小坐盘陀石。又南踰峻岭。用浩,文应后。余三人寻见性庵。路极险。屡屈折乃得。从庵降数十步。得十丈飞泉。植杖静观。乃下入内院。二人者惫卧西楼矣。既食日尚早。二人欲留。持国不可。遂行东登大岭道。望寂灭窟。石状苍然如画。傍有庵今废云。从岭头乍降。折而北登。登降者数。悬岸细路。履之凛然。宿弥陀庵。丙寅观窟。窟极奇诡。岩姿特秀。余于是叹其见之
持国,尹龙见。从石溪往。所谓虎尾将军者亦从。取道云兴洞天。泉声树影。清幽可喜。吊废寺宿狮子庵。甲子僧进酒。令携而从之。踰岭坐草行杯。酒半请文应歌。虎尾能和。路险不通马。虎尾有马。使迤行待于大芚。历曹溪食安寂庵。庵萧洒窈窕。清坐不忍去。庵僧引路。循溪而下。往往有奇处。辄静憩澄虑然后乃去。几及大芚店百步。澄潭翠壁益奇。觉昔者之游未尽也。至店虎尾果待。食红蓲𦶀。咸曰佛池清赏。不可无酒。命僧携壶前行。南踰峻岭。西见千尺削石。偃謇如相识。其窦有水。不源不流。但见滴滴下坠。所谓佛池也。满地黄金甚怪。用浩曰石中铁液。理或然欤。僧酌酒。文应歌数阕。日且夕矣。宿成佛庵。愁蝎不寐。满窗月色甚宜。乙丑至圆寂庵。虎尾辞去。庵前谷深。水清石白。小坐盘陀石。又南踰峻岭。用浩,文应后。余三人寻见性庵。路极险。屡屈折乃得。从庵降数十步。得十丈飞泉。植杖静观。乃下入内院。二人者惫卧西楼矣。既食日尚早。二人欲留。持国不可。遂行东登大岭道。望寂灭窟。石状苍然如画。傍有庵今废云。从岭头乍降。折而北登。登降者数。悬岸细路。履之凛然。宿弥陀庵。丙寅观窟。窟极奇诡。岩姿特秀。余于是叹其见之痴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6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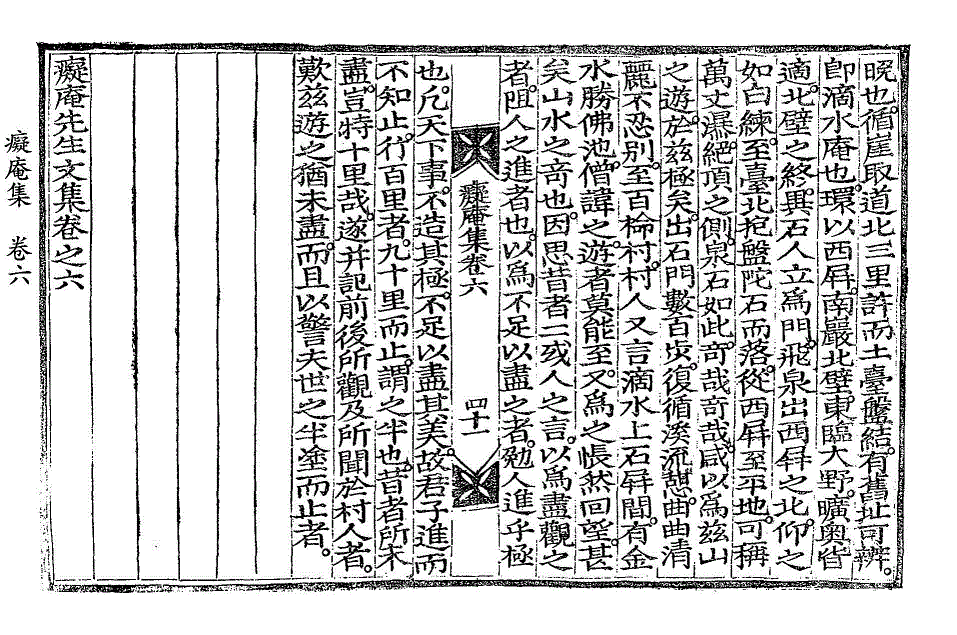 晚也。循崖取道北三里许而土台盘结。有旧址可辨。即滴水庵也。环以西屏。南岩北壁。东临大野。旷奥皆适。北壁之终。异石人立为门。飞泉出西屏之北。仰之如白练。至台北抱盘陀石而落。从西屏至平地。可称万丈瀑。绝顶之侧。泉石如此。奇哉奇哉。咸以为玆山之游。于玆极矣。出石门数百步。复循溪流憩。曲曲清丽不忍别。至百椧村。村人又言滴水上石屏间。有金水胜佛池。僧讳之。游者莫能至。又为之怅然回望。甚矣山水之奇也。因思昔者二或人之言。以为尽观之者。阻人之进者也。以为不足以尽之者。勉人进乎极也。凡天下事。不造其极。不足以尽其美。故君子进而不知止。行百里者。九十里而止。谓之半也。昔者所未尽。岂特十里哉。遂并记前后所观及所闻于村人者。叹玆游之犹未尽。而且以警夫世之半涂而止者。
晚也。循崖取道北三里许而土台盘结。有旧址可辨。即滴水庵也。环以西屏。南岩北壁。东临大野。旷奥皆适。北壁之终。异石人立为门。飞泉出西屏之北。仰之如白练。至台北抱盘陀石而落。从西屏至平地。可称万丈瀑。绝顶之侧。泉石如此。奇哉奇哉。咸以为玆山之游。于玆极矣。出石门数百步。复循溪流憩。曲曲清丽不忍别。至百椧村。村人又言滴水上石屏间。有金水胜佛池。僧讳之。游者莫能至。又为之怅然回望。甚矣山水之奇也。因思昔者二或人之言。以为尽观之者。阻人之进者也。以为不足以尽之者。勉人进乎极也。凡天下事。不造其极。不足以尽其美。故君子进而不知止。行百里者。九十里而止。谓之半也。昔者所未尽。岂特十里哉。遂并记前后所观及所闻于村人者。叹玆游之犹未尽。而且以警夫世之半涂而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