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讲议
讲议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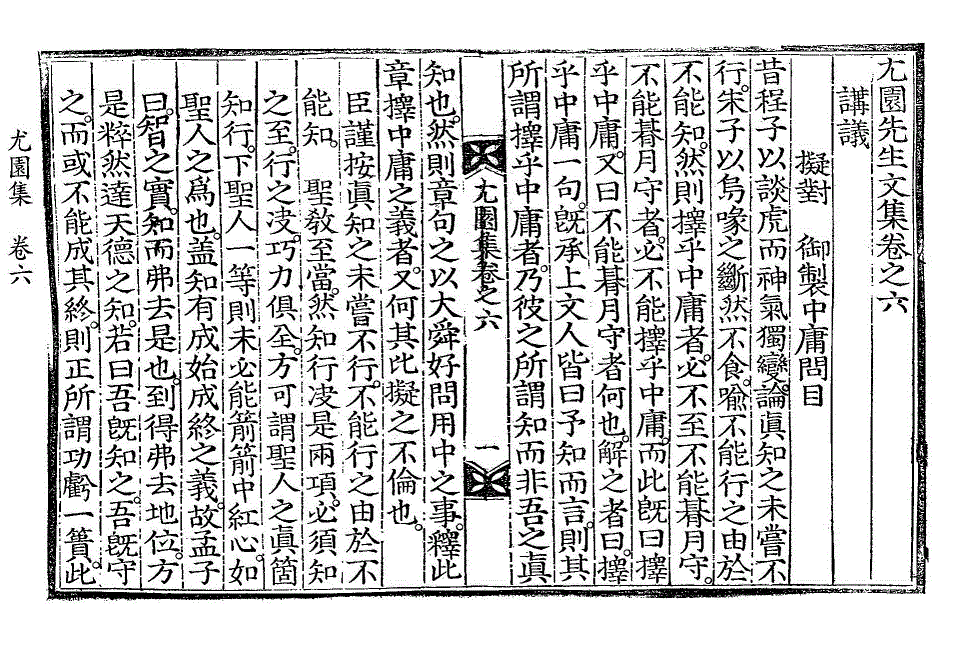 拟对 御制中庸问目
拟对 御制中庸问目昔程子以谈虎而神气独变。论真知之未尝不行。朱子以乌喙之断然不食。喻不能行之由于不能知。然则择乎中庸者。必不至不能期月守。不能期月守者。必不能择乎中庸。而此既曰择乎中庸。又曰不能期月守者何也。解之者曰。择乎中庸一句。既承上文人皆曰予知而言。则其所谓择乎中庸者。乃彼之所谓知而非吾之真知也。然则章句之以大舜好问用中之事。释此章择中庸之义者。又何其比拟之不伦也。
臣谨按真知之未尝不行。不能行之由于不能知。 圣教至当。然知行决是两项。必须知之至。行之决。巧力俱全。方可谓圣人之真个知行。下圣人一等则未必能箭箭中红心。如圣人之为也。盖知有成始成终之义。故孟子曰。智之实。知而弗去是也。到得弗去地位。方是粹然达天德之知。若曰吾既知之。吾既守之。而或不能成其终。则正所谓功亏一篑。此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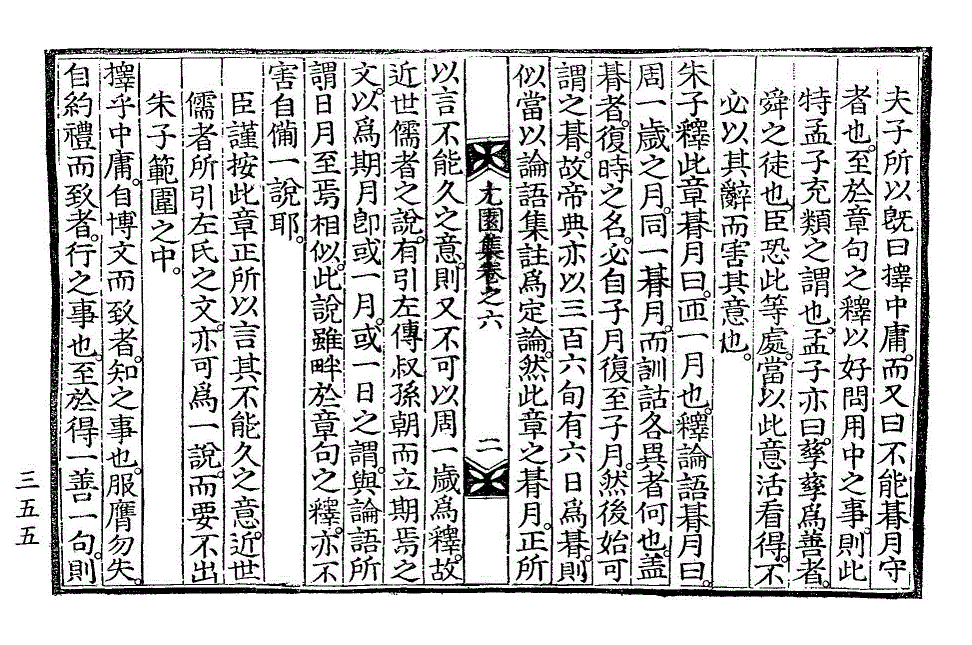 夫子所以既曰择中庸。而又曰不能期月守者也。至于章句之释以好问用中之事。则此特孟子充类之谓也。孟子亦曰。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臣恐此等处。当以此意活看得。不必以其辞而害其意也。
夫子所以既曰择中庸。而又曰不能期月守者也。至于章句之释以好问用中之事。则此特孟子充类之谓也。孟子亦曰。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臣恐此等处。当以此意活看得。不必以其辞而害其意也。朱子释此章期月曰。匝一月也。释论语期月曰。周一岁之月。同一期月。而训诂各异者何也。盖期者。复时之名。必自子月复至子月。然后始可谓之期。故帝典亦以三百六旬有六日为期。则似当以论语集注为定论。然此章之期月。正所以言不能久之意。则又不可以周一岁为释。故近世儒者之说。有引左传叔孙朝而立期焉之文。以为期月即或一月。或一日之谓。与论语所谓日月至焉相似。此说虽畔于章句之释。亦不害自备一说耶。
臣谨按此章正所以言其不能久之意。近世儒者所引左氏之文。亦可为一说。而要不出朱子范围之中。
择乎中庸。自博文而致者。知之事也。服膺勿失。自约礼而致者。行之事也。至于得一善一句。则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6H 页
 当属之知耶。属之行耶。以为行也则却在拳拳服膺之前。以为知也则得之一字。便有行道有得之意。然则不属知。不属行。而别有此一等境界耶。
当属之知耶。属之行耶。以为行也则却在拳拳服膺之前。以为知也则得之一字。便有行道有得之意。然则不属知。不属行。而别有此一等境界耶。臣谨按知行相资。知之明则行益力。行之力则知益尽。盖此得字。属知亦得。属行亦得。初非知行外别般境界。但当交致其功。足目俱到者。自当默识。恐不可悬想揣度。排布境界。徒费辞说而无益于实得也。
六章言大舜之知。而朱子以为行底意多。此章言颜子之仁。而朱子以为知底意多。其意可详言欤。六章先言问察而后言用中。此章先言择中而后言服膺。其先知后行。未尝有异。而朱子之必如是分言者何也。
臣谨按前章有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而不遗底意思。故曰行底意多。此章有仰高钻坚。欲罢不能底意思。故曰知底意多。至于上下两章。先知后行。 圣教至当。而此篇大旨。以舜,颜渊,子路之知仁勇。分以言之。故朱子之意。又就其分言之中。以明其知而行行而知也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6L 页
 欤。
欤。国家之可均。爵禄之可辞。白刃之可蹈。章句以为知仁勇之事。其分贴之义。可得闻欤。一匡天下。再许其仁则均天下者。独不可为仁乎。不俟终曰。知几其神则辞爵禄者。独不可为知乎。大抵此三者。秖是就天下之事。举其至难者。以明中庸之为至难者而已。不必泥贴于知仁勇。然后始于经旨为安。章句此释。终不无愤悱。何以看则为得。
臣谨按。此章大旨。秖是举三者之至难。以明中庸之为尤难也。或问已有此说。而章句曰。亦知仁勇之事。亦之为言。初非贴属于真个知仁勇也。盖就此三者。因其近似而分属之。故陈北溪亦曰。不必泥说知仁勇。盖朱子之加一亦字。而曰知仁勇之事者。正所以预防后人之泥著说了。惟在善读者以意而深体之。方不失立言正意耳。吾夫子称管仲之仁。特就事功上说。而小器不知礼之评。已是决案。至若不俟终日。知几其神。是圣人分上事。则恐不可容易称之于洁身长往之伦也。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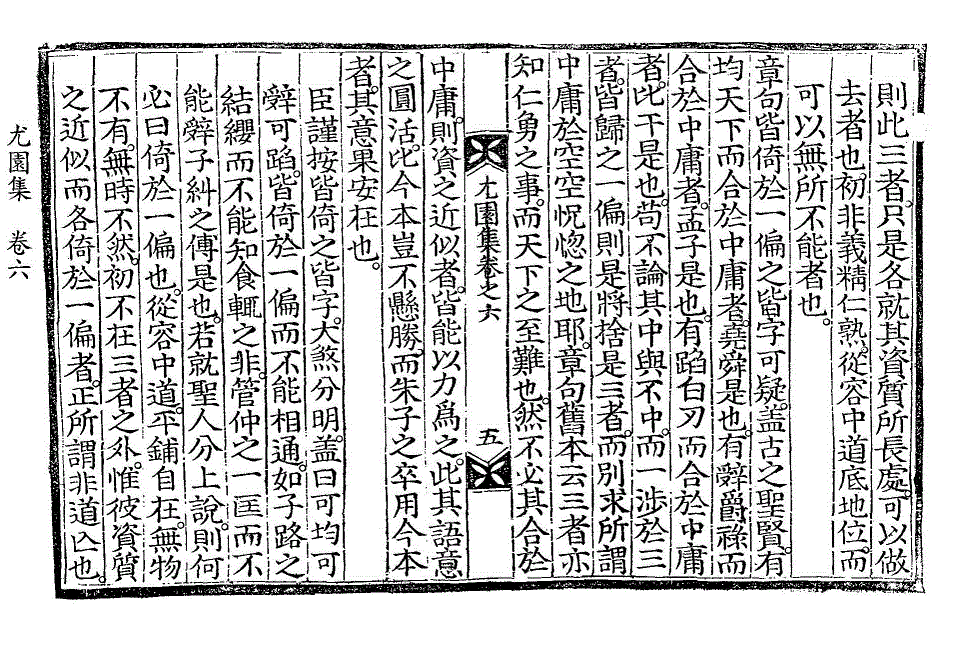 则此三者。只是各就其资质所长处。可以做去者也。初非义精仁熟。从容中道底地位。而可以无所不能者也。
则此三者。只是各就其资质所长处。可以做去者也。初非义精仁熟。从容中道底地位。而可以无所不能者也。章句皆倚于一偏之皆字可疑。盖古之圣贤。有均天下而合于中庸者。尧舜是也。有辞爵禄而合于中庸者。孟子是也。有蹈白刃而合于中庸者。比干是也。苟不论其中与不中。而一涉于三者。皆归之一偏则是将舍是三者。而别求所谓中庸于空空恍惚之地耶。章句旧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而天下之至难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则资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此其语意之圆活。比今本岂不悬胜。而朱子之卒用今本者。其意果安在也。
臣谨按皆倚之皆字。大煞分明。盖曰可均可辞可蹈。皆倚于一偏而不能相通。如子路之结缨而不能知食辄之非。管仲之一匡而不能辞子纠之傅是也。若就圣人分上说。则何必曰倚于一偏也。从容中道。平铺自在。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初不在三者之外。惟彼资质之近似而各倚于一偏者。正所谓非道亡也。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7L 页
 幽厉不由也。伏惟 圣躬勉焉。至于旧本之不用。则不必其合于中庸一句。比诸今本。终欠十分打决。恐不若今本之分晓。又可以发明不合之端矣。朱子之意。无乃以此耶。
幽厉不由也。伏惟 圣躬勉焉。至于旧本之不用。则不必其合于中庸一句。比诸今本。终欠十分打决。恐不若今本之分晓。又可以发明不合之端矣。朱子之意。无乃以此耶。可均之均。章句以平治释之。然则此章之均天下国家。即大学之治国平天下也。大学之治平则为明新之止至善。此章之均天下则不得为中庸之道者何也。岂至善与中庸。果有不同耶。
臣谨按。此与大学不同者。此不过为资质之偏长。而大学为明新之极功故也。
先天之方位。乾居于南。坤居于北。乾刚而坤柔。乾健而坤顺。则南方之风气。宜乎刚劲而反柔弱。北方之风气。宜乎柔弱而反刚劲者何也。且刚柔劲弱。不易之对待也。北方之刚劲。南方之柔弱。既若是相反而同归于强。则所谓不能强者。果在于何处耶。
臣谨按南柔北刚。饶氏体刚用柔。体柔用刚之说。载在注脚。且南北强之称。是不过就其风气中论其所谓强者如斯而已。论此者惟当察其气质之用小。学问之功大。和以处众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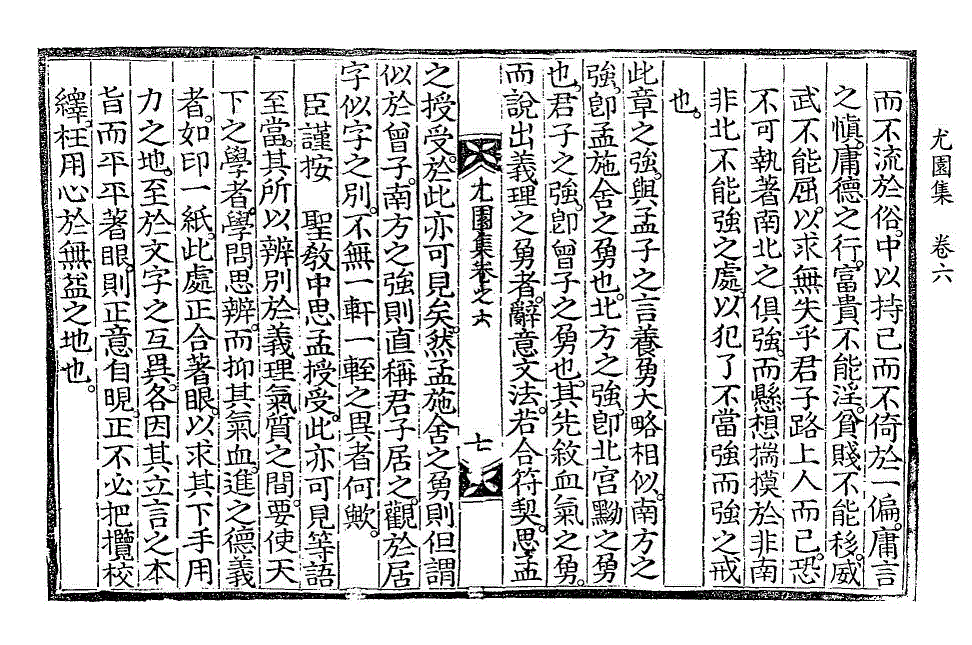 而不流于俗。中以持己而不倚于一偏。庸言之慎。庸德之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求无失乎君子路上人而已。恐不可执著南北之俱强。而悬想揣摸于非南非北不能强之处。以犯了不当强而强之戒也。
而不流于俗。中以持己而不倚于一偏。庸言之慎。庸德之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求无失乎君子路上人而已。恐不可执著南北之俱强。而悬想揣摸于非南非北不能强之处。以犯了不当强而强之戒也。此章之强。与孟子之言养勇大略相似。南方之强。即孟施舍之勇也。北方之强。即北宫黝之勇也。君子之强。即曾子之勇也。其先叙血气之勇。而说出义理之勇者。辞意文法。若合符契。思,孟之授受。于此亦可见矣。然孟施舍之勇则但谓似于曾子。南方之强则直称君子居之。观于居字似字之别。不无一轩一轾之异者何欤。
臣谨按 圣教中思孟授受。此亦可见等语至当。其所以辨别于义理气质之间。要使天下之学者。学问思辨。而抑其气血。进之德义者。如印一纸。此处正合著眼。以求其下手用力之地。至于文字之互异。各因其立言之本旨而平平著眼。则正意自晛。正不必把揽校绎。枉用心于无益之地也。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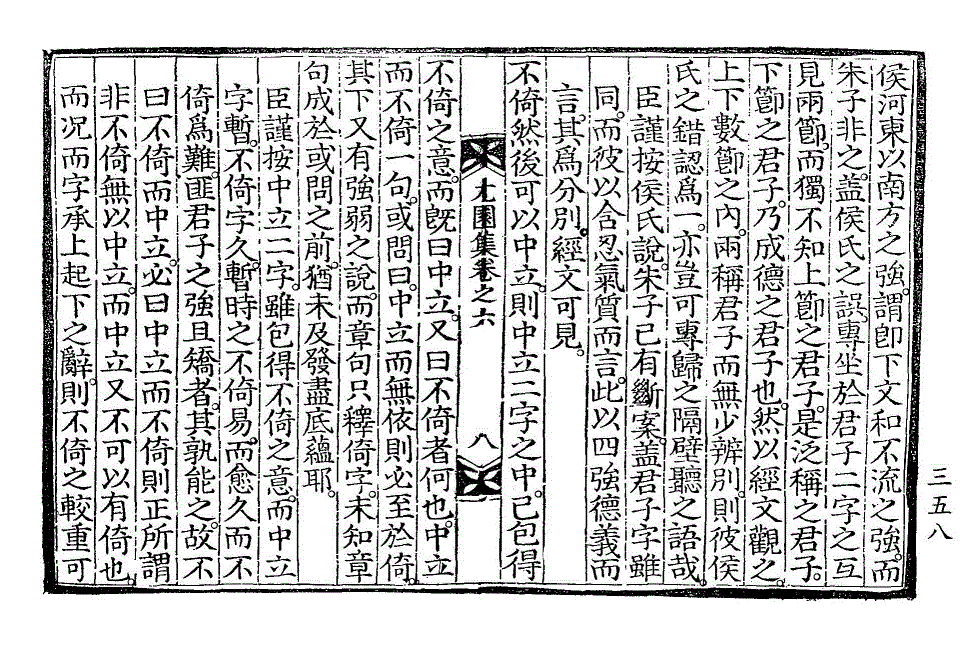 侯河东以南方之强。谓即下文和不流之强。而朱子非之。盖侯氏之误。专坐于君子二字之互见两节。而独不知上节之君子。是泛称之君子。下节之君子。乃成德之君子也。然以经文观之。上下数节之内。两称君子而无少辨别。则彼侯氏之错认为一。亦岂可专归之隔壁听之语哉。
侯河东以南方之强。谓即下文和不流之强。而朱子非之。盖侯氏之误。专坐于君子二字之互见两节。而独不知上节之君子。是泛称之君子。下节之君子。乃成德之君子也。然以经文观之。上下数节之内。两称君子而无少辨别。则彼侯氏之错认为一。亦岂可专归之隔壁听之语哉。臣谨按侯氏说。朱子已有断案。盖君子字虽同。而彼以含忍气质而言。此以四强德义而言。其为分别。经文可见。
不倚然后可以中立。则中立二字之中。已包得不倚之意。而既曰中立。又曰不倚者何也。中立而不倚一句。或问曰。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其下又有强弱之说。而章句只释倚字。未知章句成于或问之前。犹未及发尽底蕴耶。
臣谨按中立二字。虽包得不倚之意。而中立字暂。不倚字久。暂时之不倚易。而愈久而不倚为难。匪君子之强且矫者。其孰能之。故不曰不倚而中立。必曰中立而不倚则正所谓非不倚无以中立。而中立又不可以有倚也。而况而字承上起下之辞。则不倚之较重可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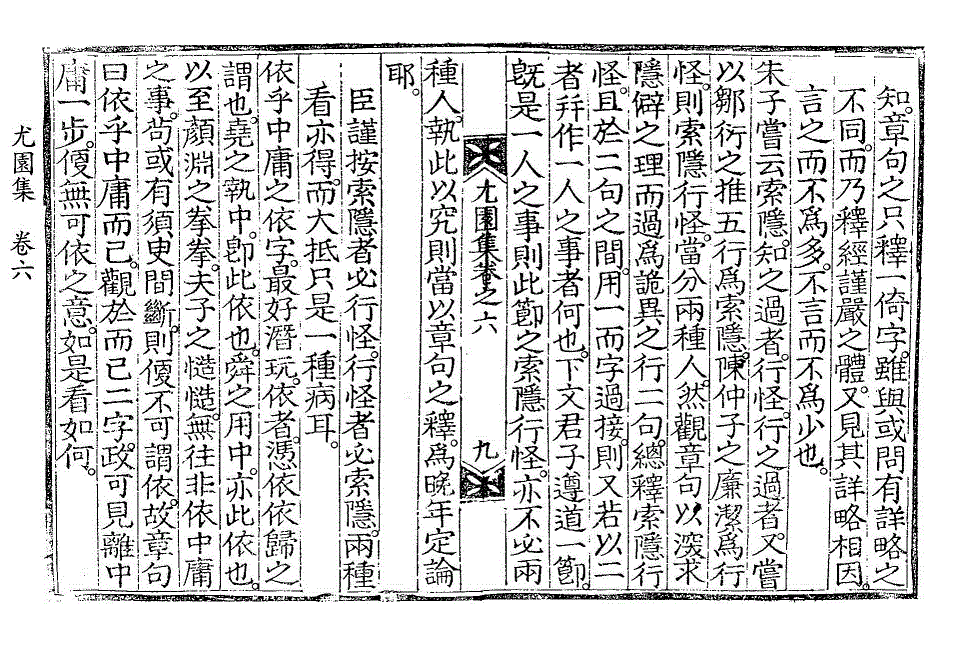 知。章句之只释一倚字。虽与或问有详略之不同。而乃释经谨严之体。又见其详略相因。言之而不为多。不言而不为少也。
知。章句之只释一倚字。虽与或问有详略之不同。而乃释经谨严之体。又见其详略相因。言之而不为多。不言而不为少也。朱子尝云索隐。知之过者。行怪。行之过者。又尝以邹衍之推五行为索隐。陈仲子之廉洁为行怪。则索隐行怪。当分两种人。然观章句以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二句。总释索隐行怪。且于二句之间。用一而字过接。则又若以二者并作一人之事者何也。下文君子遵道一节。既是一人之事则此节之索隐行怪。亦不必两种人。执此以究则当以章句之释。为晚年定论耶。
臣谨按索隐者必行怪。行怪者必索隐。两种看亦得。而大抵只是一种病耳。
依乎中庸之依字。最好潜玩。依者。凭依依归之谓也。尧之执中。即此依也。舜之用中。亦此依也。以至颜渊之拳拳。夫子之慥慥。无往非依中庸之事。苟或有须臾间断。则便不可谓依。故章句曰依乎中庸而已。观于而已二字。政可见离中庸一步。便无可依之意。如是看如何。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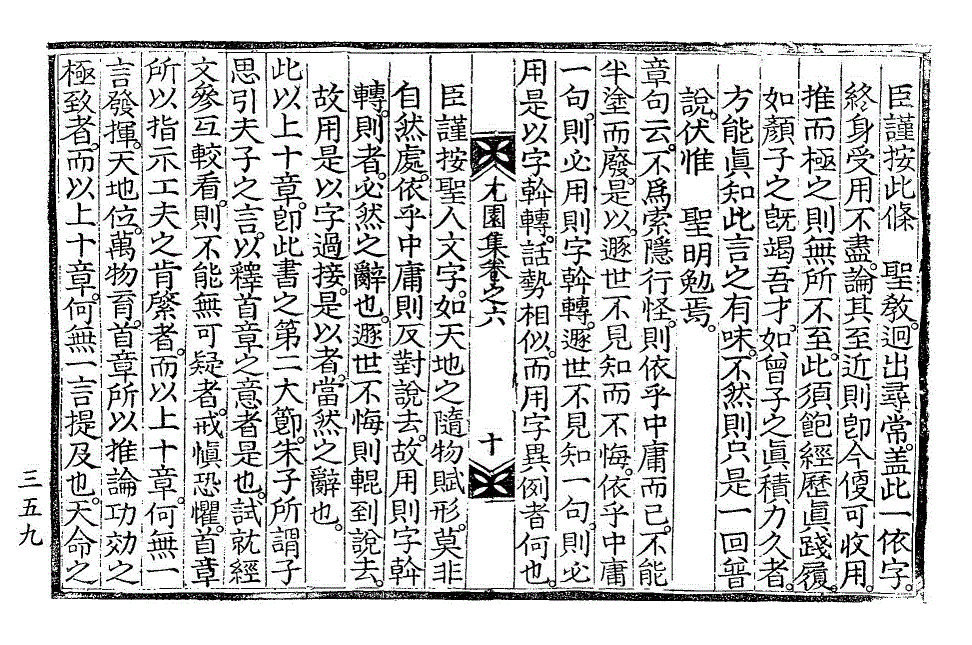 臣谨按此条 圣教。迥出寻常。盖此一依字。终身受用不尽。论其至近则即今便可收用。推而极之则无所不至。此须饱经历真践履。如颜子之既竭吾才。如曾子之真积力久者。方能真知此言之有味。不然则只是一回普说。伏惟 圣明勉焉。
臣谨按此条 圣教。迥出寻常。盖此一依字。终身受用不尽。论其至近则即今便可收用。推而极之则无所不至。此须饱经历真践履。如颜子之既竭吾才。如曾子之真积力久者。方能真知此言之有味。不然则只是一回普说。伏惟 圣明勉焉。章句云。不为索隐行怪。则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涂而废。是以。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依乎中庸一句。则必用则字斡转。遁世不见知一句。则必用是以字斡转。话势相似。而用字异例者何也。
臣谨按圣人文字。如天地之随物赋形。莫非自然处。依乎中庸则反对说去。故用则字斡转。则者。必然之辞也。遁世不悔则辊到说去。故用是以字过接。是以者。当然之辞也。
此以上十章。即此书之第二大节。朱子所谓子思引夫子之言。以释首章之意者是也。试就经文参互较看。则不能无可疑者。戒慎恐惧。首章所以指示工夫之肯綮者。而以上十章。何无一言发挥。天地位。万物育。首章所以推论功效之极致者。而以上十章。何无一言提及也。天命之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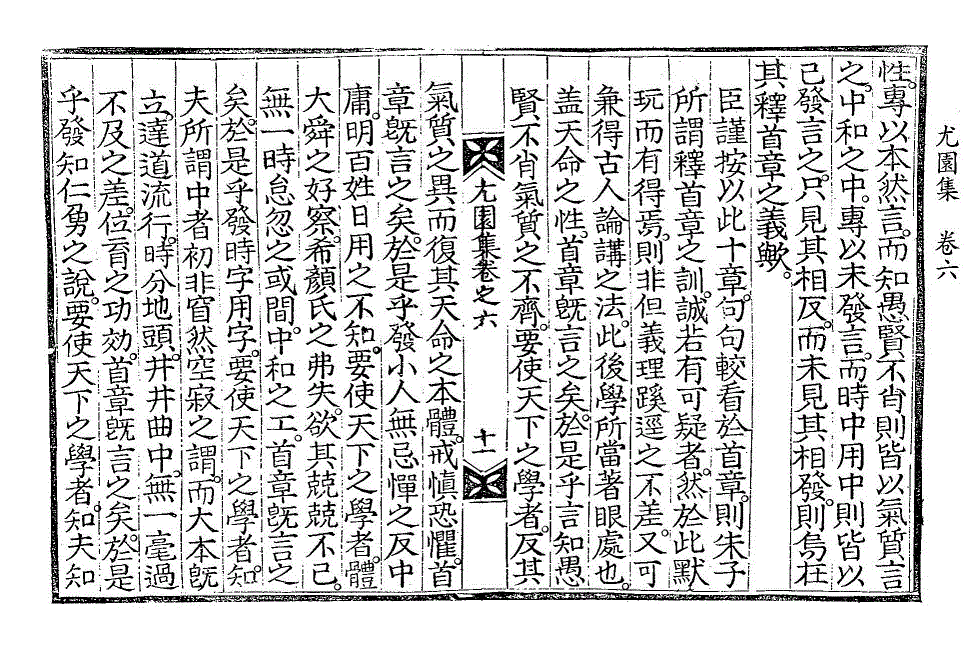 性。专以本然言。而知愚贤不肖则皆以气质言之。中和之中。专以未发言。而时中用中则皆以已发言之。只见其相反。而未见其相发。则乌在其释首章之义欤。
性。专以本然言。而知愚贤不肖则皆以气质言之。中和之中。专以未发言。而时中用中则皆以已发言之。只见其相反。而未见其相发。则乌在其释首章之义欤。臣谨按以此十章。句句较看于首章。则朱子所谓释首章之训。诚若有可疑者。然于此默玩而有得焉。则非但义理蹊径之不差。又可兼得古人论讲之法。此后学所当著眼处也。盖天命之性。首章既言之矣。于是乎言知愚贤不肖气质之不齐。要使天下之学者。反其气质之异而复其天命之本体。戒慎恐惧。首章既言之矣。于是乎发小人无忌惮之反中庸。明百姓日用之不知。要使天下之学者。体大舜之好察。希颜氏之弗失。欲其兢兢不已。无一时怠忽之或间。中和之工。首章既言之矣。于是乎发时字用字。要使天下之学者。知夫所谓中者初非窅然空寂之谓。而大本既立。达道流行。时分地头。井井曲中。无一毫过不及之差。位育之功效。首章既言之矣。于是乎发知仁勇之说。要使天下之学者。知夫知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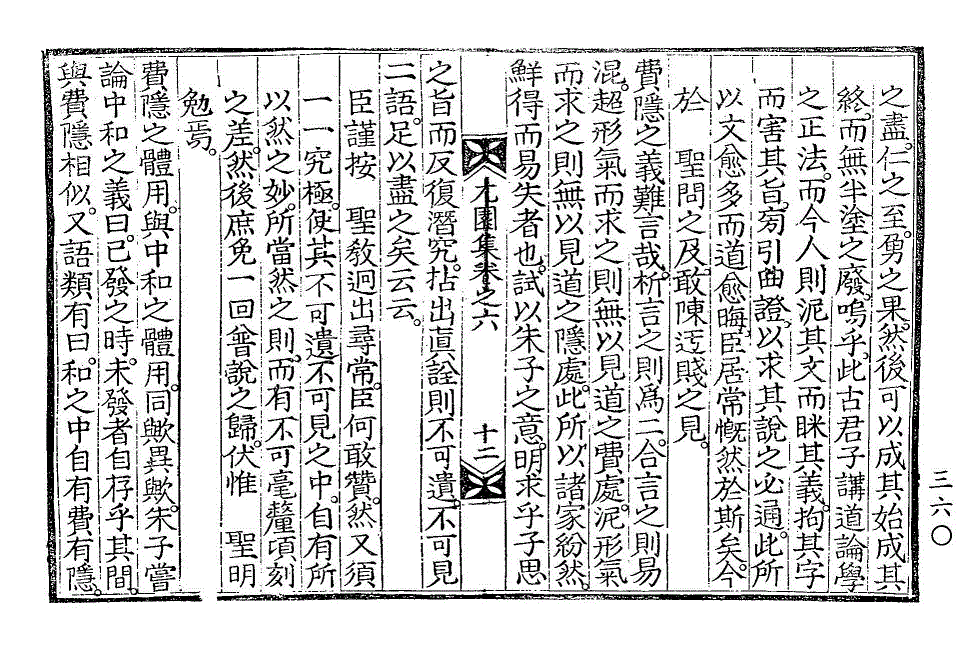 之尽。仁之至。勇之果。然后可以成其始成其终。而无半涂之废。呜乎。此古君子讲道论学之正法。而今人则泥其文而眯其义。拘其字而害其旨。旁引曲證。以求其说之必通。此所以文愈多而道愈晦。臣居常慨然于斯矣。今于 圣问之及。敢陈迂贱之见。
之尽。仁之至。勇之果。然后可以成其始成其终。而无半涂之废。呜乎。此古君子讲道论学之正法。而今人则泥其文而眯其义。拘其字而害其旨。旁引曲證。以求其说之必通。此所以文愈多而道愈晦。臣居常慨然于斯矣。今于 圣问之及。敢陈迂贱之见。费隐之义难言哉。析言之则为二。合言之则易混。超形气而求之则无以见道之费处。泥形气而求之则无以见道之隐处。此所以诸家纷然。鲜得而易失者也。试以朱子之意。明求乎子思之旨而反复潜究。拈出真诠则不可遗。不可见二语。足以尽之矣云云。
臣谨按 圣教迥出寻常。臣何敢赞。然又须一一究极。使其不可遗不可见之中。自有所以然之妙。所当然之则。而有不可毫釐顷刻之差。然后庶免一回普说之归。伏惟 圣明勉焉。
费隐之体用。与中和之体用。同欤异欤。朱子尝论中和之义曰。已发之时。未发者自存乎其间。与费隐相似。又语类有曰。和之中自有费有隐。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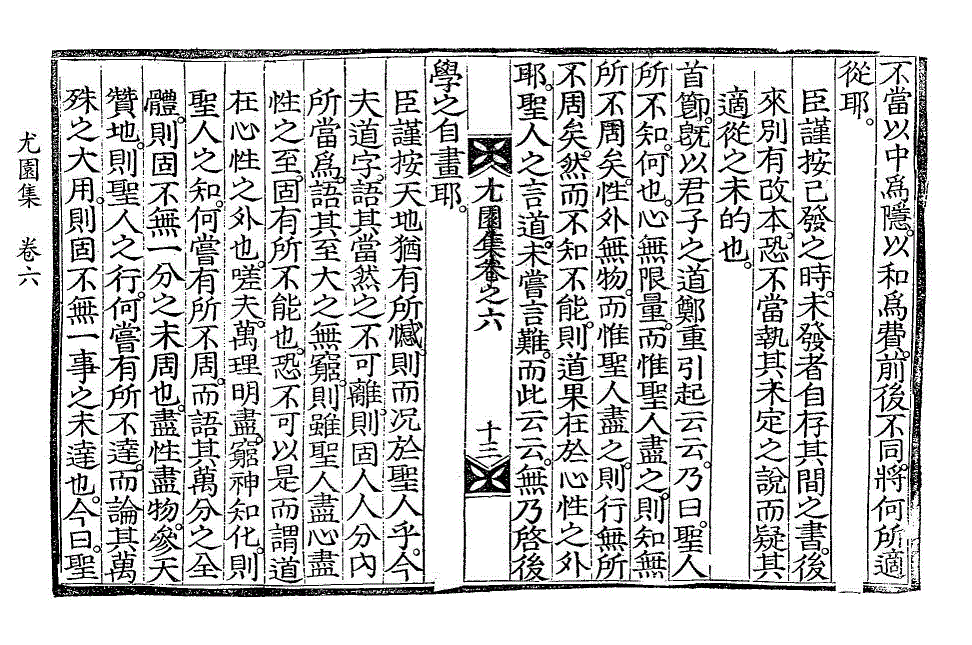 不当以中为隐。以和为费。前后不同。将何所适从耶。
不当以中为隐。以和为费。前后不同。将何所适从耶。臣谨按已发之时。未发者自存其间之书。后来别有改本。恐不当执其未定之说而疑其适从之未的也。
首节。既以君子之道郑重引起云云。乃曰。圣人所不知。何也。心无限量。而惟圣人尽之。则知无所不周矣。性外无物。而惟圣人尽之。则行无所不周矣。然而不知不能。则道果在于心性之外耶。圣人之言道。未尝言难。而此云云。无乃启后学之自画耶。
臣谨按天地犹有所憾。则而况于圣人乎。今夫道字。语其当然之不可离。则固人人分内所当为。语其至大之无穷。则虽圣人尽心尽性之至。固有所不能也。恐不可以是而谓道在心性之外也。嗟夫。万理明尽。穷神知化。则圣人之知。何尝有所不周。而语其万分之全体。则固不无一分之未周也。尽性尽物。参天赞地。则圣人之行。何尝有所不达。而论其万殊之大用。则固不无一事之未达也。今曰。圣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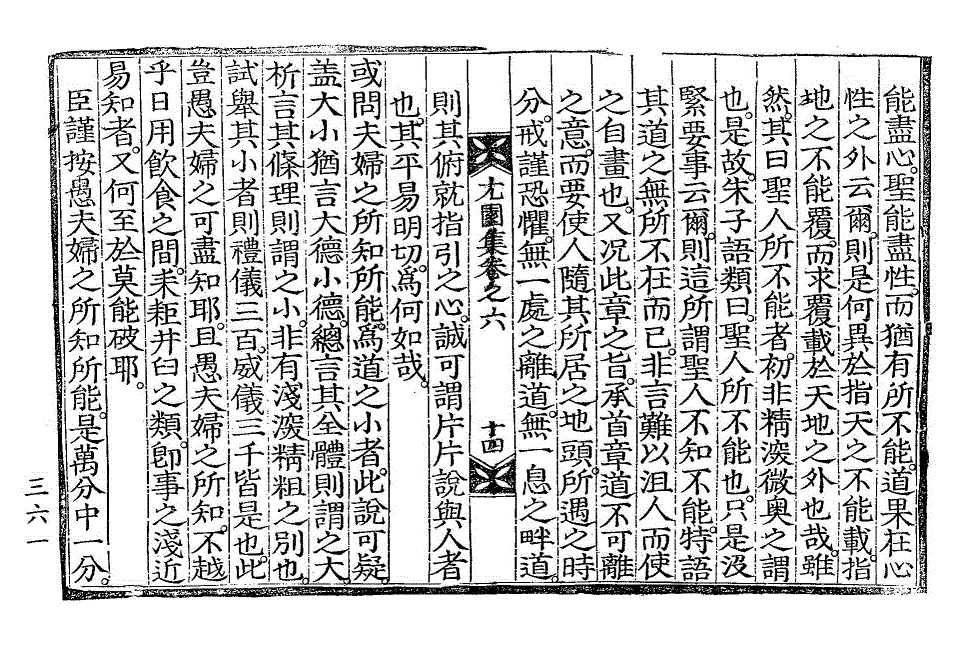 能尽心。圣能尽性。而犹有所不能。道果在心性之外云尔。则是何异于指天之不能载。指地之不能覆。而求覆载于天地之外也哉。虽然。其曰圣人所不能者。初非精深微奥之谓也。是故。朱子语类曰。圣人所不能也。只是没紧要事云尔。则这所谓圣人不知不能。特语其道之无所不在而已。非言难以沮人而使之自画也。又况此章之旨。承首章道不可离之意。而要使人随其所居之地头。所遇之时分。戒谨恐惧。无一处之离道。无一息之畔道。则其俯就指引之心。诚可谓片片说与人者也。其平易明切。为何如哉。
能尽心。圣能尽性。而犹有所不能。道果在心性之外云尔。则是何异于指天之不能载。指地之不能覆。而求覆载于天地之外也哉。虽然。其曰圣人所不能者。初非精深微奥之谓也。是故。朱子语类曰。圣人所不能也。只是没紧要事云尔。则这所谓圣人不知不能。特语其道之无所不在而已。非言难以沮人而使之自画也。又况此章之旨。承首章道不可离之意。而要使人随其所居之地头。所遇之时分。戒谨恐惧。无一处之离道。无一息之畔道。则其俯就指引之心。诚可谓片片说与人者也。其平易明切。为何如哉。或问夫妇之所知所能。为道之小者。此说可疑。盖大小犹言大德小德。总言其全体则谓之大。析言其条理则谓之小。非有浅深精粗之别也。试举其小者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皆是也。此岂愚夫妇之可尽知耶。且愚夫妇之所知。不越乎日用饮食之间。耒耟并臼之类。即事之浅近易知者。又何至于莫能破耶。
臣谨按愚夫妇之所知所能。是万分中一分。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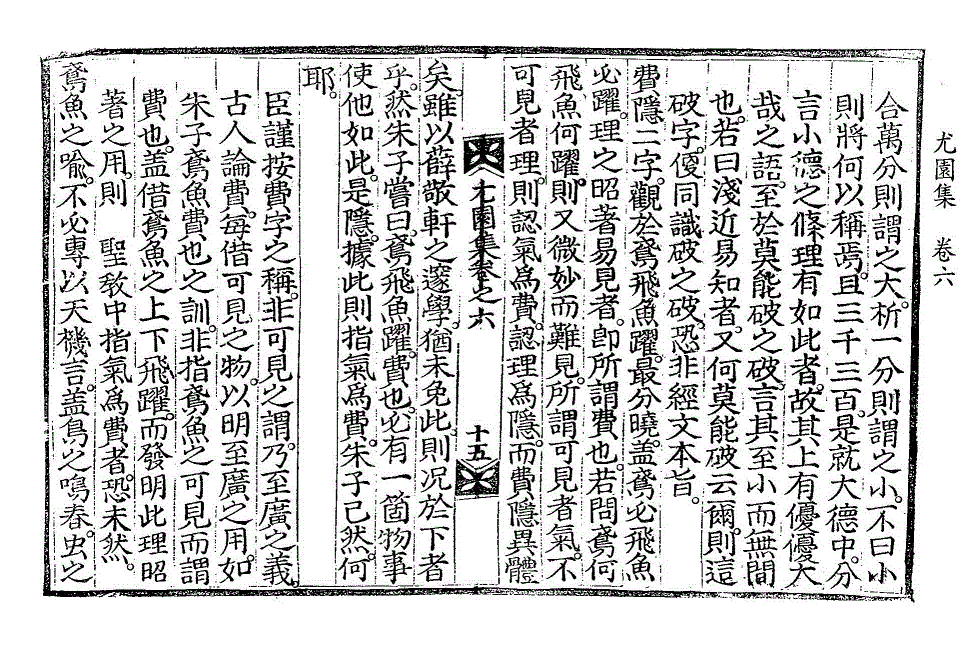 合万分则谓之大。析一分则谓之小。不曰小则将何以称焉。且三千三百。是就大德中。分言小德之条理有如此者。故其上有优优大哉之语。至于莫能破之破。言其至小而无间也。若曰浅近易知者。又何莫能破云尔。则这破字。便同识破之破。恐非经文本旨。
合万分则谓之大。析一分则谓之小。不曰小则将何以称焉。且三千三百。是就大德中。分言小德之条理有如此者。故其上有优优大哉之语。至于莫能破之破。言其至小而无间也。若曰浅近易知者。又何莫能破云尔。则这破字。便同识破之破。恐非经文本旨。费隐二字。观于鸢飞鱼跃。最分晓。盖鸢必飞鱼必跃。理之昭著易见者。即所谓费也。若问鸢何飞鱼何跃。则又微妙而难见。所谓可见者气。不可见者理。则认气为费。认理为隐。而费隐异体矣。虽以薛敬轩之邃学。犹未免此。则况于下者乎。然朱子尝曰。鸢飞鱼跃。费也。必有一个物事使他如此。是隐。据此则指气为费。朱子已然。何耶。
臣谨按费字之称。非可见之谓。乃至广之义。古人论费。每借可见之物。以明至广之用。如朱子鸢鱼费也之训。非指鸢鱼之可见而谓费也。盖借鸢鱼之上下飞跃。而发明此理昭著之用。则 圣教中指气为费者。恐未然。
鸢鱼之喻。不必专以天机言。盖鸟之鸣春。虫之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2L 页
 鸣秋。何莫非天机之发。而必取鸢鱼。所以形容上下昭著之理也。朱子尝曰。鸢飞鱼跃。言此理之发见。恰似禅家青青绿竹。莫非真如。灿灿黄花。莫非般若之语。但彼言发见一切混乱。吾儒所言。须辨其定分。鸢必飞天。鱼必跃渊。执此以观。则此一节。自兼流行定分二义。苟或专就流行说。则便与禅家无辨。然上蔡以上下察。只明道体之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其意似若主流行。而朱子称其极精。何也。
鸣秋。何莫非天机之发。而必取鸢鱼。所以形容上下昭著之理也。朱子尝曰。鸢飞鱼跃。言此理之发见。恰似禅家青青绿竹。莫非真如。灿灿黄花。莫非般若之语。但彼言发见一切混乱。吾儒所言。须辨其定分。鸢必飞天。鱼必跃渊。执此以观。则此一节。自兼流行定分二义。苟或专就流行说。则便与禅家无辨。然上蔡以上下察。只明道体之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其意似若主流行。而朱子称其极精。何也。臣谨按不必专言天机。 圣教至当。盖非独鸢鱼上见天机故也。吾儒释家之似同不同。彼则一回普说而全无伦序。如绿竹黄花之说也。此则流行昭著而上下各定。如鸢鱼上下之喻是也。上蔡非指鸢鱼等语。实是超然独见于言意之表。其下文又曰。上下各得云尔。则其语意之精密。宜乎见赞于朱子。而非若禅家话头也明矣。
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故鸢飞鱼跃之理。实具于吾身方寸之间。日用云为。动静语默。莫非此理呈露处。程子所谓与必有事而勿正之意。同活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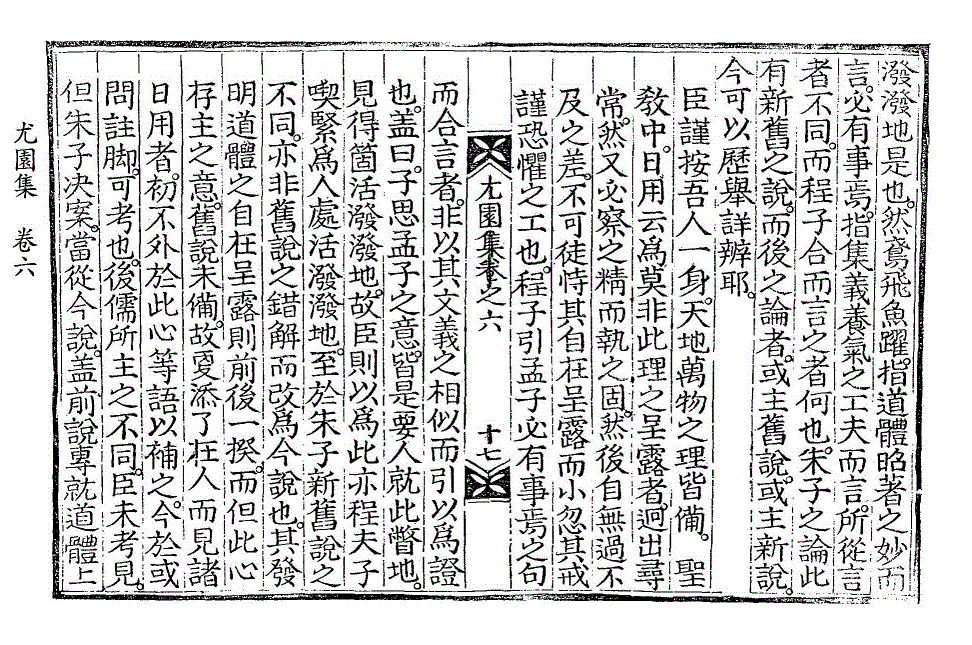 泼泼地是也。然鸢飞鱼跃。指道体昭著之妙而言。必有事焉。指集义养气之工夫而言。所从言者不同。而程子合而言之者何也。朱子之论此有新旧之说。而后之论者。或主旧说。或主新说。今可以历举详辨耶。
泼泼地是也。然鸢飞鱼跃。指道体昭著之妙而言。必有事焉。指集义养气之工夫而言。所从言者不同。而程子合而言之者何也。朱子之论此有新旧之说。而后之论者。或主旧说。或主新说。今可以历举详辨耶。臣谨按吾人一身。天地万物之理皆备。 圣教中。日用云为莫非此理之呈露者。迥出寻常。然又必察之精而执之固。然后自无过不及之差。不可徒恃其自在呈露而小忽其戒谨恐惧之工也。程子引孟子必有事焉之句而合言者。非以其文义之相似而引以为證也。盖曰。子思孟子之意。皆是要人就此瞥地。见得个活泼泼地。故臣则以为此亦程夫子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至于朱子新旧说之不同。亦非旧说之错解而改为今说也。其发明道体之自在呈露则前后一揆。而但此心存主之意。旧说未备。故更添了在人而见诸日用者。初不外于此心等语以补之。今于或问注脚。可考也。后儒所主之不同。臣未考见。但朱子决案。当从今说。盖前说专就道体上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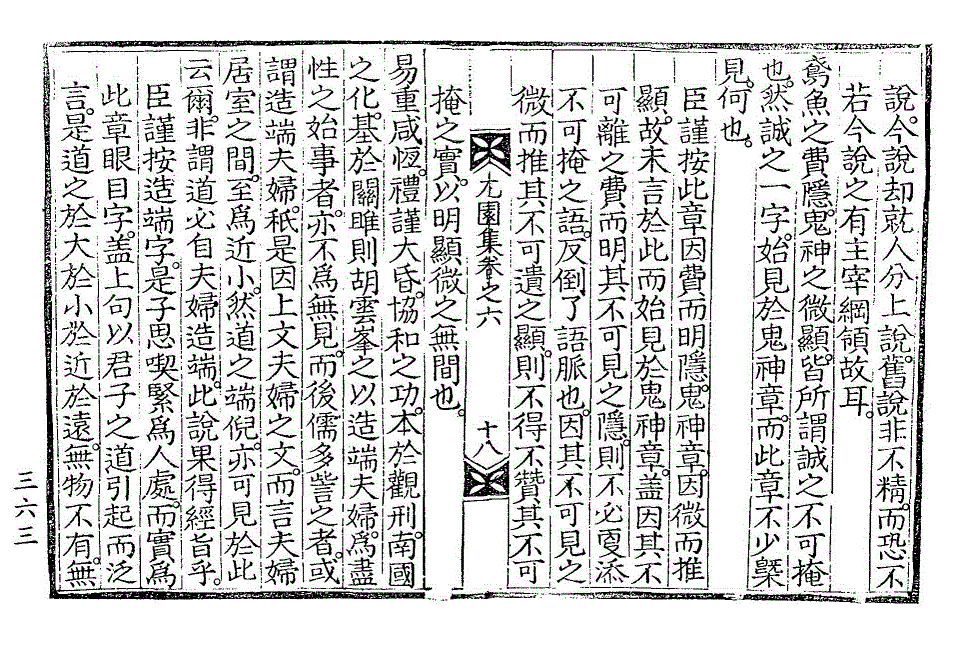 说。今说却就人分上说。旧说非不精。而恐不若今说之有主宰纲领故耳。
说。今说却就人分上说。旧说非不精。而恐不若今说之有主宰纲领故耳。鸢鱼之费隐。鬼神之微显。皆所谓诚之不可掩也。然诚之一字。始见于鬼神章。而此章不少槩见。何也。
臣谨按此章因费而明隐。鬼神章。因微而推显。故未言于此而始见于鬼神章。盖因其不可离之费而明其不可见之隐。则不必更添不可掩之语。反倒了语脉也。因其不可见之微而推其不可遗之显。则不得不赞其不可掩之实。以明显微之无间也。
易重咸恒。礼谨大昏。协和之功。本于观刑。南国之化。基于关雎则胡云峰之以造端夫妇。为尽性之始事者。亦不为无见。而后儒多訾之者。或谓造端夫妇。秖是因上文夫妇之文。而言夫妇居室之间。至为近小。然道之端倪。亦可见于此云尔。非谓道必自夫妇造端。此说果得经旨乎。
臣谨按造端字。是子思吃紧为人处。而实为此章眼目字。盖上句以君子之道引起而泛言。是道之于大于小于近于远。无物不有。无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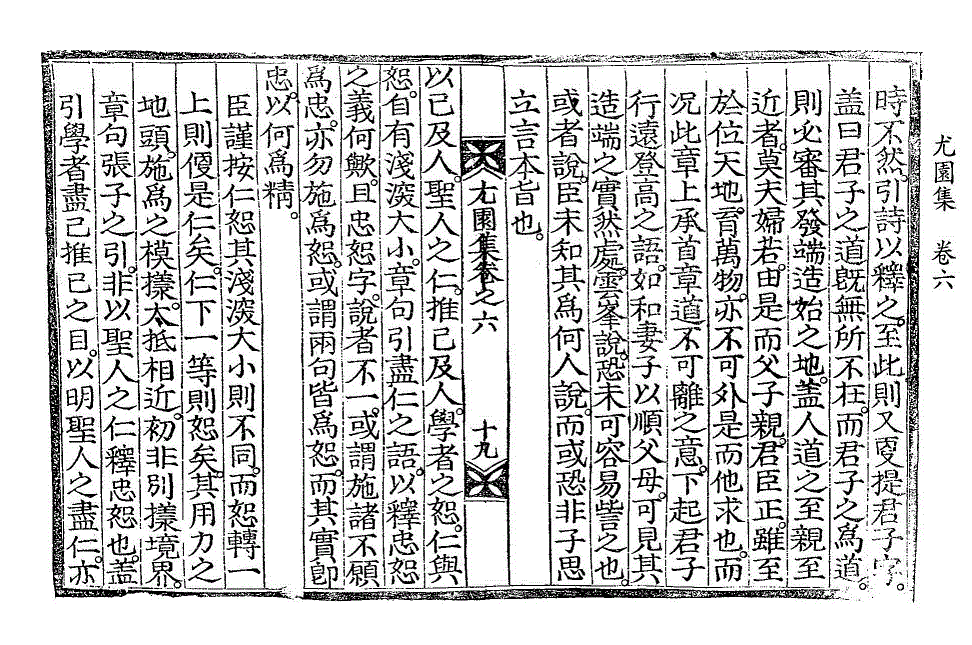 时不然。引诗以释之。至此则又更提君子字。盖曰君子之道既无所不在。而君子之为道。则必审其发端造始之地。盖人道之至亲至近者。莫夫妇若。由是而父子亲君臣正。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亦不可外是而他求也。而况此章上承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下起君子行远登高之语。如和妻子以顺父母。可见其造端之实然处。云峰说。恐未可容易訾之也。或者说。臣未知其为何人说。而或恐非子思立言本旨也。
时不然。引诗以释之。至此则又更提君子字。盖曰君子之道既无所不在。而君子之为道。则必审其发端造始之地。盖人道之至亲至近者。莫夫妇若。由是而父子亲君臣正。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亦不可外是而他求也。而况此章上承首章道不可离之意。下起君子行远登高之语。如和妻子以顺父母。可见其造端之实然处。云峰说。恐未可容易訾之也。或者说。臣未知其为何人说。而或恐非子思立言本旨也。以己及人。圣人之仁。推己及人。学者之恕。仁与恕。自有浅深大小。章句引尽仁之语。以释忠恕之义何欤。且忠恕字。说者不一。或谓施诸不愿为忠。亦勿施为恕。或谓两句皆为恕。而其实即忠。以何为精。
臣谨按仁恕其浅深大小则不同。而恕转一上则便是仁矣。仁下一等则恕矣。其用力之地头。施为之模㨾。太抵相近。初非别㨾境界。章句张子之引。非以圣人之仁释忠恕也。盖引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明圣人之尽仁。亦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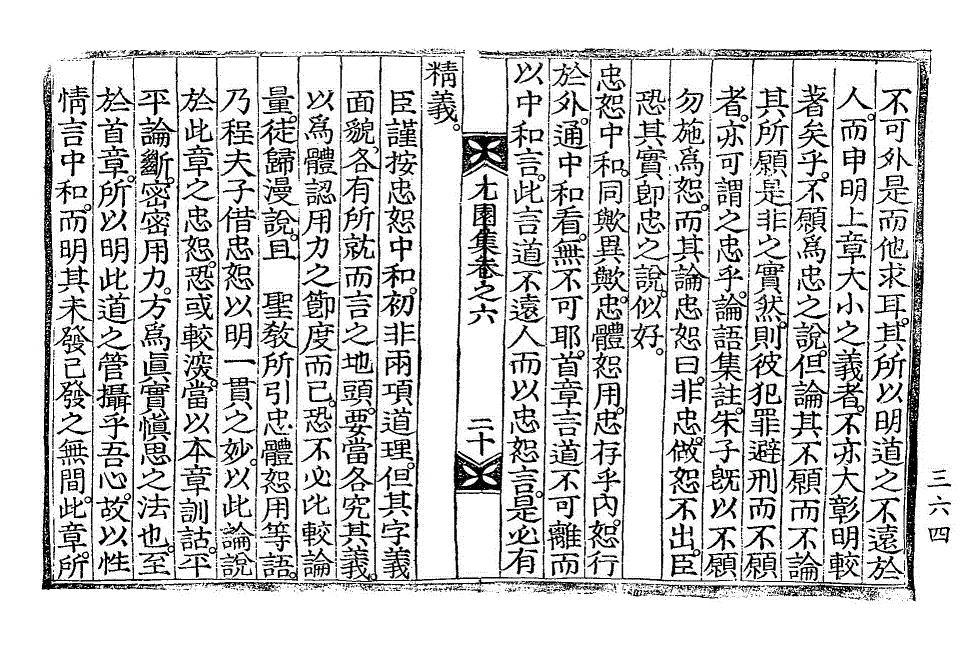 不可外是而他求耳。其所以明道之不远于人。而申明上章大小之义者。不亦大彰明较著矣乎。不愿为忠之说。但论其不愿而不论其所愿是非之实然。则彼犯罪避刑而不愿者。亦可谓之忠乎。论语集注。朱子既以不愿勿施为恕。而其论忠恕曰。非忠。做恕不出。臣恐其实即忠之说。似好。
不可外是而他求耳。其所以明道之不远于人。而申明上章大小之义者。不亦大彰明较著矣乎。不愿为忠之说。但论其不愿而不论其所愿是非之实然。则彼犯罪避刑而不愿者。亦可谓之忠乎。论语集注。朱子既以不愿勿施为恕。而其论忠恕曰。非忠。做恕不出。臣恐其实即忠之说。似好。忠恕中和。同欤异欤。忠体恕用。忠存乎内。恕行于外。通中和看。无不可耶。首章言道不可离而以中和言。此言道不远人而以忠恕言。是必有精义。
臣谨按忠恕中和。初非两项道理。但其字义面貌。各有所就而言之地头。要当各究其义。以为体认用力之节度而已。恐不必比较论量。徒归漫说。且 圣教所引忠体恕用等语。乃程夫子借忠恕以明一贯之妙。以此论说于此章之忠恕。恐或较深。当以本章训诂。平平论断。密密用力。方为真实慎思之法也。至于首章。所以明此道之管摄乎吾心。故以性情言中和。而明其未发已发之无间。此章。所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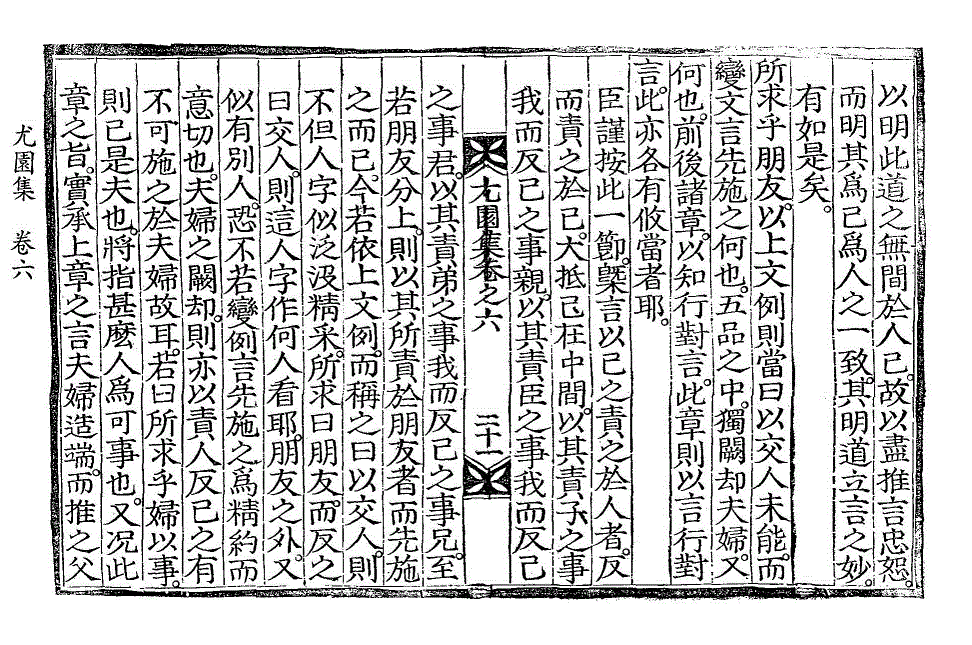 以明此道之无间于人己。故以尽推言忠恕。而明其为己为人之一致。其明道立言之妙。有如是矣。
以明此道之无间于人己。故以尽推言忠恕。而明其为己为人之一致。其明道立言之妙。有如是矣。所求乎朋友。以上文例则当曰以交人未能。而变文言先施之何也。五品之中。独阙却夫妇。又何也。前后诸章。以知行对言。此章则以言行对言。此亦各有攸当者耶。
臣谨按此一节。槩言以己之责之于人者。反而责之于己。大抵已在中间。以其责子之事我而反己之事亲。以其责臣之事我而反己之事君。以其责弟之事我而反己之事兄。至若朋友分上。则以其所责于朋友者而先施之而已。今若依上文例。而称之曰以交人。则不但人字似泛没精采。所求曰朋友。而反之曰交人。则这人字作何人看耶。朋友之外。又似有别人。恐不若变例言先施之为精约而意切也。夫妇之阙却。则亦以责人反己之有不可施之于夫妇故耳。若曰所求乎妇以事。则已是夫也。将指甚么人为可事也。又况此章之旨。实承上章之言夫妇造端。而推之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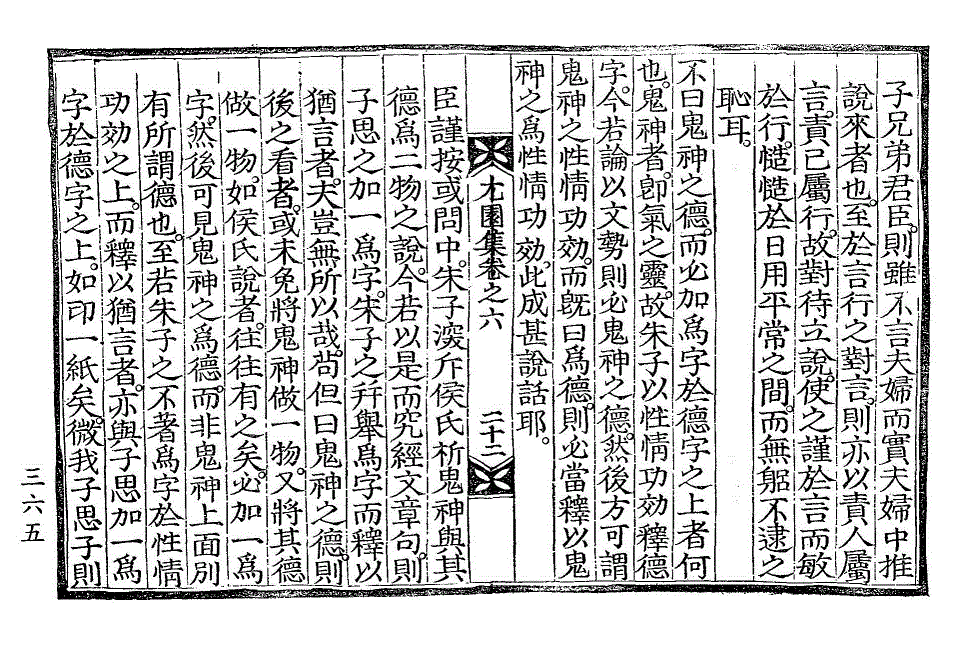 子兄弟君臣。则虽不言夫妇而实夫妇中推说来者也。至于言行之对言。则亦以责人属言。责己属行。故对待立说。使之谨于言而敏于行。慥慥于日用平常之间。而无躬不逮之耻耳。
子兄弟君臣。则虽不言夫妇而实夫妇中推说来者也。至于言行之对言。则亦以责人属言。责己属行。故对待立说。使之谨于言而敏于行。慥慥于日用平常之间。而无躬不逮之耻耳。不曰鬼神之德。而必加为字于德字之上者何也。鬼神者。即气之灵。故朱子以性情功效释德字。今若论以文势则必鬼神之德。然后方可谓鬼神之性情功效。而既曰为德。则必当释以鬼神之为性情功效。此成甚说话耶。
臣谨按或问中。朱子深斥侯氏析鬼神与其德为二物之说。今若以是而究经文章句。则子思之加一为字。朱子之并举为字而释以犹言者。夫岂无所以哉。苟但曰鬼神之德。则后之看者。或未免将鬼神做一物。又将其德做一物。如侯氏说者。往往有之矣。必加一为字。然后可见鬼神之为德。而非鬼神上面别有所谓德也。至若朱子之不著为字于性情功效之上。而释以犹言者。亦与子思加一为字于德字之上。如印一纸矣。微我子思子则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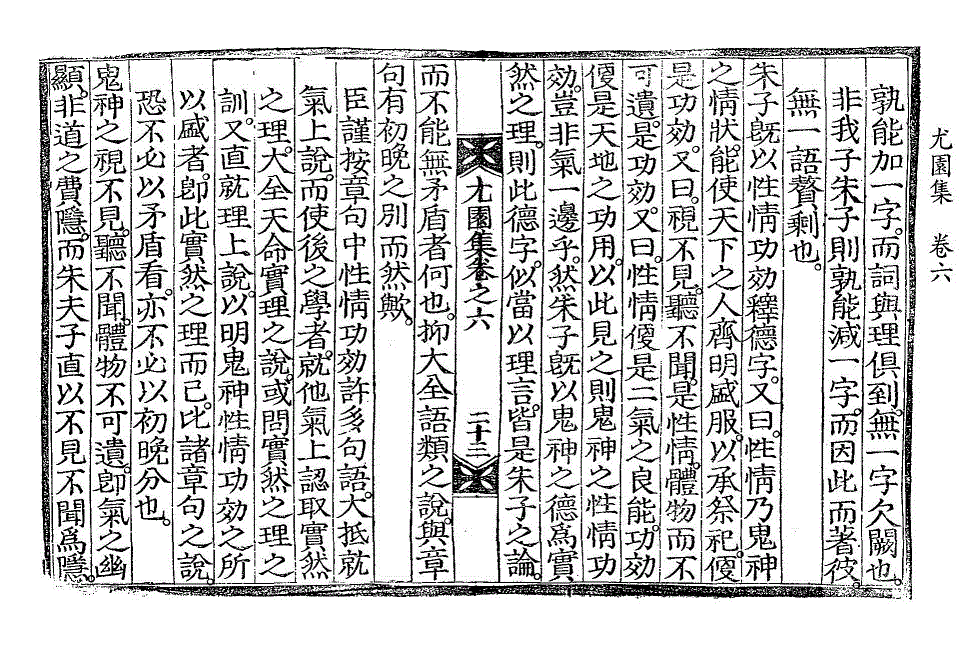 孰能加一字。而词与理俱到。无一字欠阙也。非我子朱子则孰能减一字。而因此而著彼。无一语赘剩也。
孰能加一字。而词与理俱到。无一字欠阙也。非我子朱子则孰能减一字。而因此而著彼。无一语赘剩也。朱子既以性情功效释德字。又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状。能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又曰。视不见。听不闻。是性情。体物而不可遗。是功效。又曰。性情便是二气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以此见之则鬼神之性情功效。岂非气一边乎。然朱子既以鬼神之德为实然之理。则此德字。似当以理言。皆是朱子之论。而不能无矛盾者何也。抑大全语类之说。与章句有初晚之别而然欤。
臣谨按章句中性情功效许多句语。大抵就气上说。而使后之学者。就他气上认取实然之理。大全天命实理之说。或问实然之理之训。又直就理上说。以明鬼神性情功效之所以盛者。即此实然之理而已。比诸章句之说。恐不必以矛盾看。亦不必以初晚分也。
鬼神之视不见。听不闻。体物不可遗。即气之幽显。非道之费隐。而朱夫子直以不见不闻为隐。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6L 页
 体物如在为费者。何也。
体物如在为费者。何也。臣谨按朱子费隐之分释。盖即气之幽显。明道之费隐。而举其可知可言之气。推其难知难言之道耳。
亲亲尊贤等杀即仁义礼。而独不言智者何也。下文之知人知天。即所谓智也。通上下文而言之。则可谓备言仁义礼智之德欤。抑知觉为气之灵。智为性之贞。则知不可以谓智欤。
臣谨按知亲亲尊贤之等杀。而各尽其则。这便是智。是故。孟子曰。智之实。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然则虽不言智。智自在矣。况下文之知天知人。不啻丁宁乎。知觉为气之灵。是不过知寒煖识痛痒之谓。而知天知人。是尽心知性以上事。恐不可谓气灵之知觉而不谓之智也。
知仁勇三达德。朱子以为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知底属智。行底属仁。又是朱子之论则知仁固是同得之理。而至于勇。五性之中。属于何者。而亦为同得之理欤。
臣谨按勇者。即五常健顺之健。而于五性无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7H 页
 定位。无专属。如五行之于土。无不待是而行也。是以。中庸言三近。而朱子释之曰。此三近者。勇之次。次乃次舍之次。非次等之次也。由是观之。知之至于知之一者亦勇也。行之至于成功而一者亦勇也。勇是成就结刷之谓。则虽不必专属于五性中一性。而自其气类之近似。究其条贯之所属。则恐当曰于五性属义。论语亦曰。义以为质。则勇之无专属。而实与知仁为同得之理者。又可见矣。
定位。无专属。如五行之于土。无不待是而行也。是以。中庸言三近。而朱子释之曰。此三近者。勇之次。次乃次舍之次。非次等之次也。由是观之。知之至于知之一者亦勇也。行之至于成功而一者亦勇也。勇是成就结刷之谓。则虽不必专属于五性中一性。而自其气类之近似。究其条贯之所属。则恐当曰于五性属义。论语亦曰。义以为质。则勇之无专属。而实与知仁为同得之理者。又可见矣。性字上。加一德字。说得无几于太重。学字上加一问字。话势恐归于架叠。圣人立言之微意。窃欲闻之。
臣谨按此一条。或问中程夫子及门人之说。大煞分明。有曰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一者。程夫子之说也。有曰惩忿窒欲。闲邪存其诚。此尊德性者。游广平之说也。张横渠亦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之说。盖性是天理之本然。而堕在形气之中。则其所谓性者。已不能无杂而失其粹然之本体矣。故言性而加一德字。就其形气之中。拈出其粹然不杂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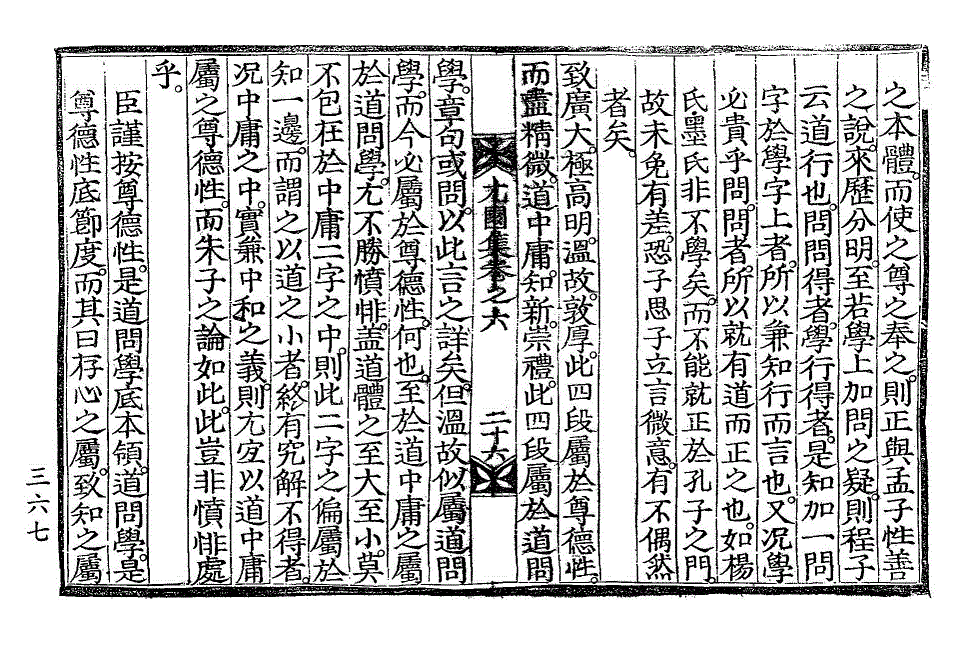 之本体。而使之尊之奉之。则正与孟子性善之说。来历分明。至若学上加问之疑。则程子云道行也。问问得者。学行得者。是知加一问字于学字上者。所以兼知行而言也。又况学必贵乎问。问者。所以就有道而正之也。如杨氏,墨氏非不学矣。而不能就正于孔子之门。故未免有差。恐子思子立言微意。有不偶然者矣。
之本体。而使之尊之奉之。则正与孟子性善之说。来历分明。至若学上加问之疑。则程子云道行也。问问得者。学行得者。是知加一问字于学字上者。所以兼知行而言也。又况学必贵乎问。问者。所以就有道而正之也。如杨氏,墨氏非不学矣。而不能就正于孔子之门。故未免有差。恐子思子立言微意。有不偶然者矣。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四段属于尊德性。而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四段属于道问学。章句或问。以此言之详矣。但温故似属道问学。而今必属于尊德性。何也。至于道中庸之属于道问学。尤不胜愤悱。盖道体之至大至小。莫不包在于中庸二字之中。则此二字之偏属于知一边。而谓之以道之小者。终有究解不得者。况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则尤宜以道中庸属之尊德性。而朱子之论如此。此岂非愤悱处乎。
臣谨按尊德性。是道问学底本领。道问学。是尊德性底节度。而其曰存心之属。致知之属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8H 页
 者。盖举行而兼知。举知而兼行也。后来陈氏有尊德性是力行工夫之说。而大为云峰之所慨然。论者不察。或以为行先于知。或疑其道中庸之偏属于知一边。或疑其温故之属于尊德性。其为后学之,蔀大矣。然则尊道之分属。此特言其大槩次序之分。以明脩德凝道之大端而已。其实欲存心者不先有以知之。则无以审其所当存者而存之。如尧舜所谓精一也。欲致知者不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则亦安能足目俱到。化与心成。而知天知命也哉。而况学之一字兼知行。故程子有笃行五者废一非学之训。今以道问学以下五句论之。尽精微属知而道中庸则行也。知新属知而崇礼则行也。恐不可谓行先于知。亦不可谓道中庸之偏于知耳。至若温故之似属道问学。程门先达如游氏,杨氏皆如此说。而大抵温燖持守之意较重。恐当属之于尊德性。如或问中细分之说。又可以该不可不知新之意矣。
者。盖举行而兼知。举知而兼行也。后来陈氏有尊德性是力行工夫之说。而大为云峰之所慨然。论者不察。或以为行先于知。或疑其道中庸之偏属于知一边。或疑其温故之属于尊德性。其为后学之,蔀大矣。然则尊道之分属。此特言其大槩次序之分。以明脩德凝道之大端而已。其实欲存心者不先有以知之。则无以审其所当存者而存之。如尧舜所谓精一也。欲致知者不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则亦安能足目俱到。化与心成。而知天知命也哉。而况学之一字兼知行。故程子有笃行五者废一非学之训。今以道问学以下五句论之。尽精微属知而道中庸则行也。知新属知而崇礼则行也。恐不可谓行先于知。亦不可谓道中庸之偏于知耳。至若温故之似属道问学。程门先达如游氏,杨氏皆如此说。而大抵温燖持守之意较重。恐当属之于尊德性。如或问中细分之说。又可以该不可不知新之意矣。温故而知新。谓旧之中更求新味之谓耶。抑故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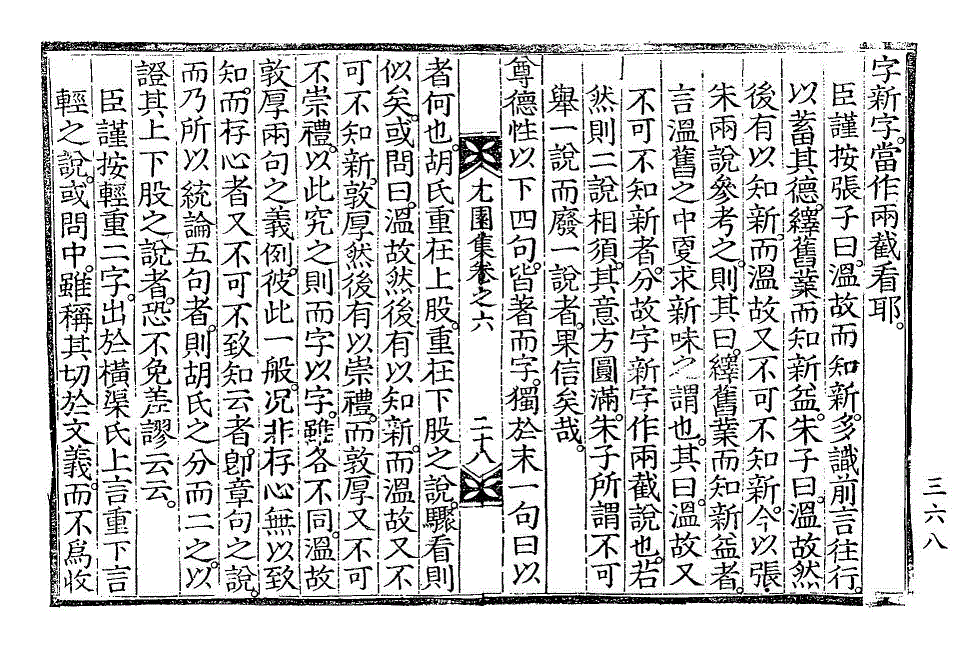 字新字。当作两截看耶。
字新字。当作两截看耶。臣谨按张子曰。温故而知新。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绎旧业而知新益。朱子曰。温故然后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今以张,朱两说参考之。则其曰。绎旧业而知新益者。言温旧之中更求新味之谓也。其曰。温故又不可不知新者。分故字新字作两截说也。若然则二说相须。其意方圆满。朱子所谓不可举一说而废一说者。果信矣哉。
尊德性以下四句。皆著而字。独于末一句曰以者何也。胡氏重在上股。重在下股之说。骤看则似矣。或问曰。温故然后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后有以崇礼。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礼。以此究之则而字以字。虽各不同。温故敦厚两句之义例。彼此一般。况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云者。即章句之说。而乃所以统论五句者。则胡氏之分而二之。以證其上下股之说者。恐不免差谬云云。
臣谨按轻重二字。出于横渠氏上言重下言轻之说。或问中。虽称其切于文义。而不为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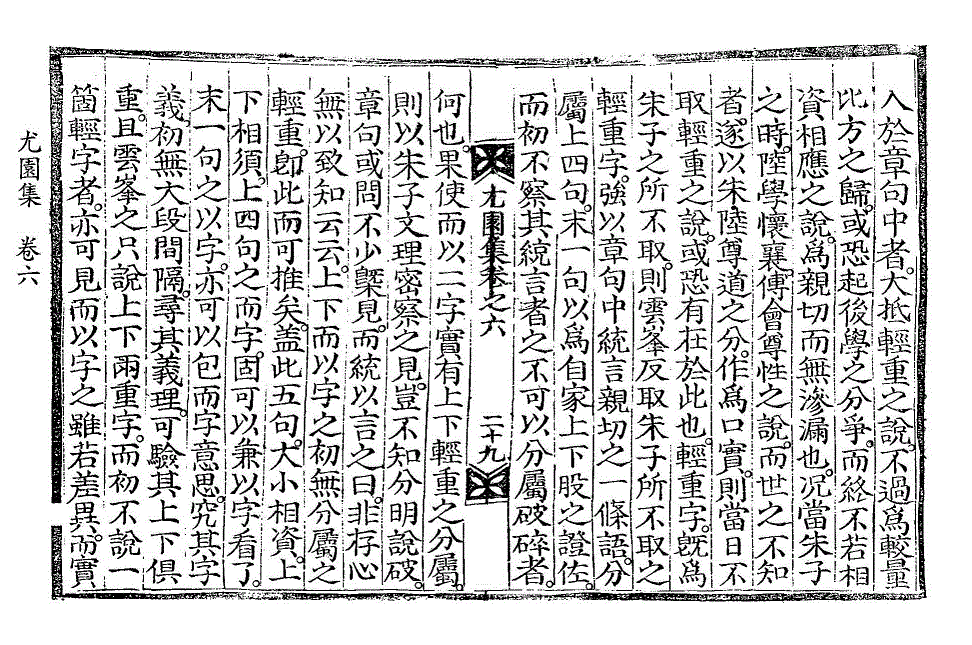 入于章句中者。大抵轻重之说。不过为较量比方之归。或恐起后学之分争。而终不若相资相应之说。为亲切而无渗漏也。况当朱子之时。陆学怀襄。傅会尊性之说。而世之不知者。遂以朱,陆尊道之分。作为口实。则当日不取轻重之说。或恐有在于此也。轻重字。既为朱子之所不取。则云峰反取朱子所不取之轻重字。强以章句中统言亲切之一条语。分属上四句。末一句以为自家上下股之證佐。而初不察其统言者之不可以分属破碎者。何也。果使而以二字实有上下轻重之分属。则以朱子文理密察之见。岂不知分明说破。章句或问不少槩见。而统以言之曰。非存心无以致知云云。上下而以字之初无分属之轻重。即此而可推矣。盖此五句。大小相资。上下相须。上四句之而字。固可以兼以字看了。末一句之以字。亦可以包而字意思。究其字义。初无大段间隔。寻其义理。可验其上下俱重。且云峰之只说上下两重字。而初不说一个轻字者。亦可见而以字之虽若差异。而实
入于章句中者。大抵轻重之说。不过为较量比方之归。或恐起后学之分争。而终不若相资相应之说。为亲切而无渗漏也。况当朱子之时。陆学怀襄。傅会尊性之说。而世之不知者。遂以朱,陆尊道之分。作为口实。则当日不取轻重之说。或恐有在于此也。轻重字。既为朱子之所不取。则云峰反取朱子所不取之轻重字。强以章句中统言亲切之一条语。分属上四句。末一句以为自家上下股之證佐。而初不察其统言者之不可以分属破碎者。何也。果使而以二字实有上下轻重之分属。则以朱子文理密察之见。岂不知分明说破。章句或问不少槩见。而统以言之曰。非存心无以致知云云。上下而以字之初无分属之轻重。即此而可推矣。盖此五句。大小相资。上下相须。上四句之而字。固可以兼以字看了。末一句之以字。亦可以包而字意思。究其字义。初无大段间隔。寻其义理。可验其上下俱重。且云峰之只说上下两重字。而初不说一个轻字者。亦可见而以字之虽若差异。而实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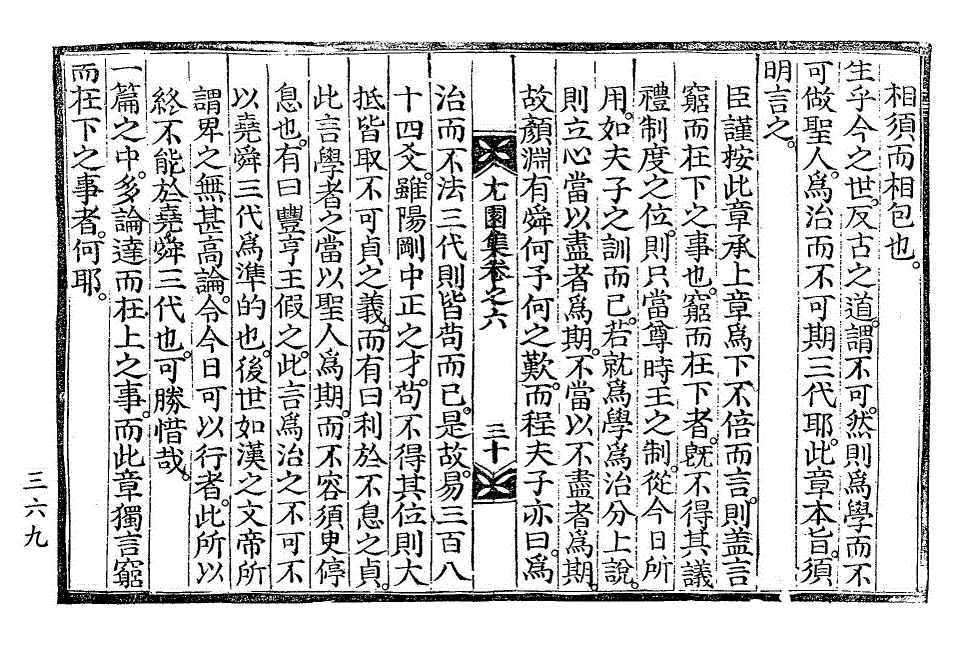 相须而相包也。
相须而相包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谓不可。然则为学而不可做圣人。为治而不可期三代耶。此章本旨。须明言之。
臣谨按此章承上章为下不倍而言。则盖言穷而在下之事也。穷而在下者。既不得其议礼制度之位。则只当尊时王之制。从今日所用。如夫子之训而已。若就为学为治分上说。则立心当以尽者为期。不当以不尽者为期。故颜渊有舜何予何之叹。而程夫子亦曰。为治而不法三代则皆苟而已。是故。易三百八十四爻。虽阳刚中正之才。苟不得其位则大抵皆取不可贞之义。而有曰利于不息之贞。此言学者之当以圣人为期。而不容须臾停息也。有曰丰亨王假之。此言为治之不可不以尧舜三代为准的也。后世如汉之文帝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令今日可以行者。此所以终不能于尧,舜三代也。可胜惜哉。
一篇之中。多论达而在上之事。而此章独言穷而在下之事者。何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0H 页
 臣谨按中庸之言穷而在下之事。非独二十八章为然。则正不必起疑于无疑。况又此章之说。所以发明上章下句未尽之意。则不得不专就在下者之事。以订其不倍之道而已。
臣谨按中庸之言穷而在下之事。非独二十八章为然。则正不必起疑于无疑。况又此章之说。所以发明上章下句未尽之意。则不得不专就在下者之事。以订其不倍之道而已。质诸鬼神而无疑。与至诚如神之意。同欤异欤。此章鬼神。与十六章鬼神一般。而朱夫子已于十六章。备释鬼神之义。则至于此章。又复释之。不嫌重复者何也。且既欲释之则阴阳之灵。似尤衬切于质而无疑之义。而不以此释之。只就程子之说。截去天地功用一句。但取造化之迹四字以释之者。何耶。
臣谨按朱子鬼神之释。虽或详或略。而各有下落。无毫发之欠剩矣。语鬼神为德之盛。故备录其功用造化。良能字屈伸字。以明其盛字之意。语鬼神已然之迹。故截取其造化之迹四个字。以订其已然可质之迹。而既曰造化之迹。则自可以该夫功用屈伸之义矣。此正如一个道字。而或兼言性之德。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或只言犹路也。盖其详略阔狭。不得不随其所言而秤量。则两章鬼神字训诂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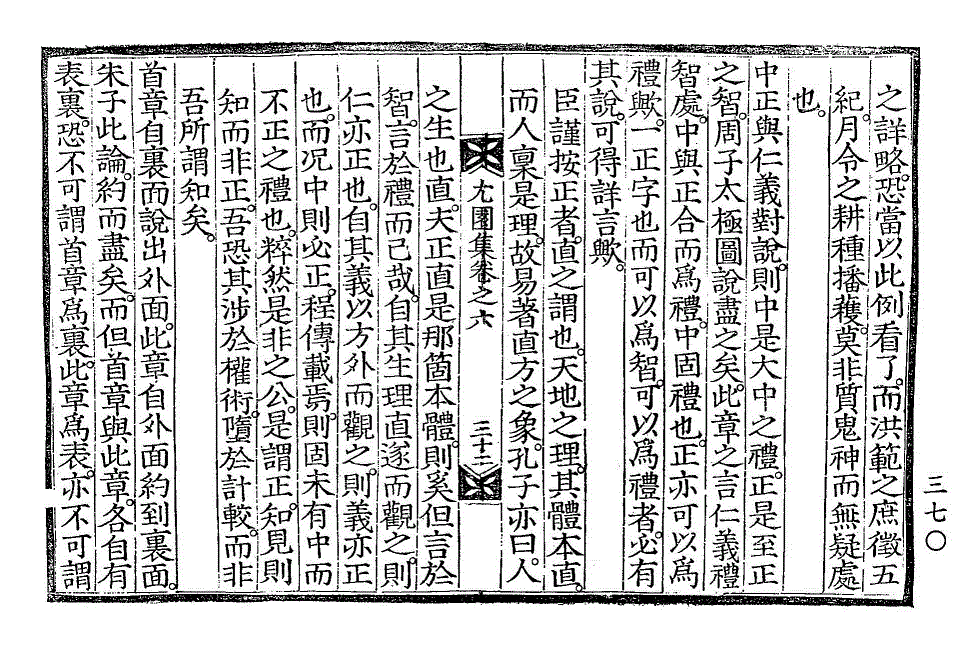 之详略。恐当以此例看了。而洪范之庶徵五纪。月令之耕种播穫。莫非质鬼神而无疑处也。
之详略。恐当以此例看了。而洪范之庶徵五纪。月令之耕种播穫。莫非质鬼神而无疑处也。中正与仁义对说。则中是大中之礼。正是至正之智。周子太极图说尽之矣。此章之言仁义礼智处。中与正合而为礼。中固礼也。正亦可以为礼欤。一正字也而可以为智。可以为礼者。必有其说。可得详言欤。
臣谨按正者。直之谓也。天地之理。其体本直。而人禀是理。故易著直方之象。孔子亦曰。人之生也直。夫正直是那个本体。则奚但言于智。言于礼而已哉。自其生理直遂而观之。则仁亦正也。自其义以方外而观之。则义亦正也。而况中则必正。程传载焉。则固未有中而不正之礼也。粹然是非之公。是谓正。知见则知而非正。吾恐其涉于权术。堕于计较。而非吾所谓知矣。
首章自里面说出外面。此章自外面约到里面。朱子此论。约而尽矣。而但首章与此章。各自有表里。恐不可谓首章为里。此章为表。亦不可谓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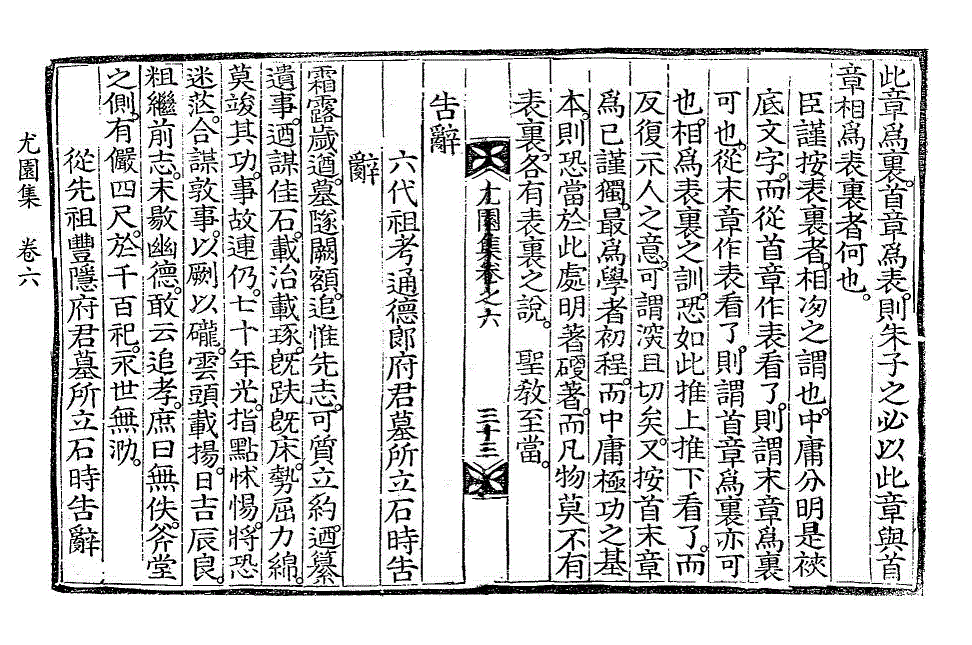 此章为里。首章为表。则朱子之必以此章与首章相为表里者何也。
此章为里。首章为表。则朱子之必以此章与首章相为表里者何也。臣谨按表里者。相吻之谓也。中庸分明是裌底文字。而从首章作表看了。则谓末章为里可也。从末章作表看了。则谓首章为里亦可也。相为表里之训。恐如此推上推下看了。而反复示人之意。可谓深且切矣。又按首末章为己谨独。最为学者初程。而中庸极功之基本。则恐当于此处明著硬著。而凡物莫不有表里。各有表里之说。 圣教至当。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告辞
六代祖考通德郎府君墓所立石时告辞
霜露岁遒。墓隧阙额。追惟先志。可质立约。乃纂遗事。乃谋佳石。载治载琢。既趺既床。势屈力绵。莫俟其功。事故连仍。七十年光。指点怵惕。将恐迷茫。合谋敦事。以劂以砻。云头载扬。日吉辰良。粗继前志。未扬幽德。敢云追孝。庶曰无佚。斧堂之侧。有俨四尺。于千百祀。永世无泐。
从先祖丰隐府君墓所立石时告辞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1L 页
 布衣死难。覆柩玆封。功传口碑。名阙褒章。有美不扬。子孙之责。荡于兵燹。家乘莫质。孤爷有录。实迹可详。是时染齿。长驱渡江。官兵义旅。望风劻勷。仡仡府君。时年七十。奋挺纠僮。忠愤激烈。截彼九潭。遏其方张。孤军一心。百弩飙飏。贼遇败逃。莫近我陵。军声遂振。代领义兵。不犯安东。曰府君功。如何不曜。不登勋券。君不识状。自古攸叹。云仍雪涕。于乎敢没。先人之志。今焉追述。购工琢石。乞文太常。篆以义将。大字炜煌。云头载扬。日吉辰良。山川改观。堂斧生色。于千百祀。永永无泐。
布衣死难。覆柩玆封。功传口碑。名阙褒章。有美不扬。子孙之责。荡于兵燹。家乘莫质。孤爷有录。实迹可详。是时染齿。长驱渡江。官兵义旅。望风劻勷。仡仡府君。时年七十。奋挺纠僮。忠愤激烈。截彼九潭。遏其方张。孤军一心。百弩飙飏。贼遇败逃。莫近我陵。军声遂振。代领义兵。不犯安东。曰府君功。如何不曜。不登勋券。君不识状。自古攸叹。云仍雪涕。于乎敢没。先人之志。今焉追述。购工琢石。乞文太常。篆以义将。大字炜煌。云头载扬。日吉辰良。山川改观。堂斧生色。于千百祀。永永无泐。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哀辞
崔毅仲哀辞
已虖。崔君毅仲。今年上春之旬。执我手而送我者非君也耶。君何入我乡而不我过。使我远于将之于锦水之阳。而瞻望伫立。涕横坠。不能自禁也。君与我俱是六十境界。其或生或死之不齐固也。而五十年从游之馀。所以相期于岁寒者。今焉已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为之歌一阕而送之曰。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2H 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仲兮。归哉归哉。已虖。崔君毅仲。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仲兮。归哉归哉。已虖。崔君毅仲。李士渐(汝鸿)哀辞
不佞固陋寡闻。晚而从寡斋李丈游。翁正直方严。乐善不倦。使人懑焉心服。因见其诸子雁序联翩。鸾鹄停峙。蔚然为邓林杞梓。而其季表德曰士渐。颖秀若发硎之铓。精笃若深丛之罴。藉藉称公车巨擘者也。翁语余曰。鸿也舞勺之年。能了解十图次第。且吾性粗峻。诸子未尝假以色辞。而于鸿则不能不肯可。父子之间。成一个朋友。翁非溺于爱者。不佞见而奇之。闻其语而蹶然。窃致其公门未艾之贺矣。士渐年三十三。擢进士。人皆以为骥步方展。而不幸病病。竟不起。呜呼惜哉。青云黄甲。命也外物也。不足为士渐恨。而以其才资之美。得其年以致其中晚之工。则岂只为今日之士渐。而乘黄蹶决云折。天也。不佞游君父子间。所以相期于晚暮者有在。而今也失之。将何辞仰慰其大人翁也。虽然。士渐有三佳儿。天之所以不尽报施于士渐者。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2L 页
 将在于斯乎。遂为之歌。一阕而送之。(以下缺。)
将在于斯乎。遂为之歌。一阕而送之。(以下缺。)柳士能(奭祚)哀辞
柳上庠士能。我母氏堂侄季存氏之仲子也。不佞往来于外门。外门诸父兄说门内后生。必称季存氏之三子。而其所刺刺不离口者。尤在于士能。士能资禀笃实。聪明出群。又善古篆。他人所模拟不得者。士能为之。随手浑成。盖不但科目奇才也。癸丑之变。讼冤于京。彼之排布声势。凛乎其可危。而士能周旋其间。不震不竦。竟使幽冤得彻。褒 命特下。此岂草茆年少者所可容易办得耶。使假之寿。充其才量。得其时而展布。则其为邦国之华。又何可量也。乙卯登上庠。弱岁蜚英。晋途方启。而不幸病不起于闻韶之寓馆。葬于冰山礼葬之原。呜呼其可惜也已。余与季存氏游。爱士能特异。而衰病相挻。不能一往哭其殡次。聊以芜辞代哭。辞曰。
谓天无心。胡为乎钟美于名家耶。谓天有心。胡为乎不并畀其寿耶。胚胎名祖之幽光。若将有为也。吁嗟乎秀而不实。严霜打之。岂命物者亦有所主张。不得于腾倒不齐者耶。父母兮俱存。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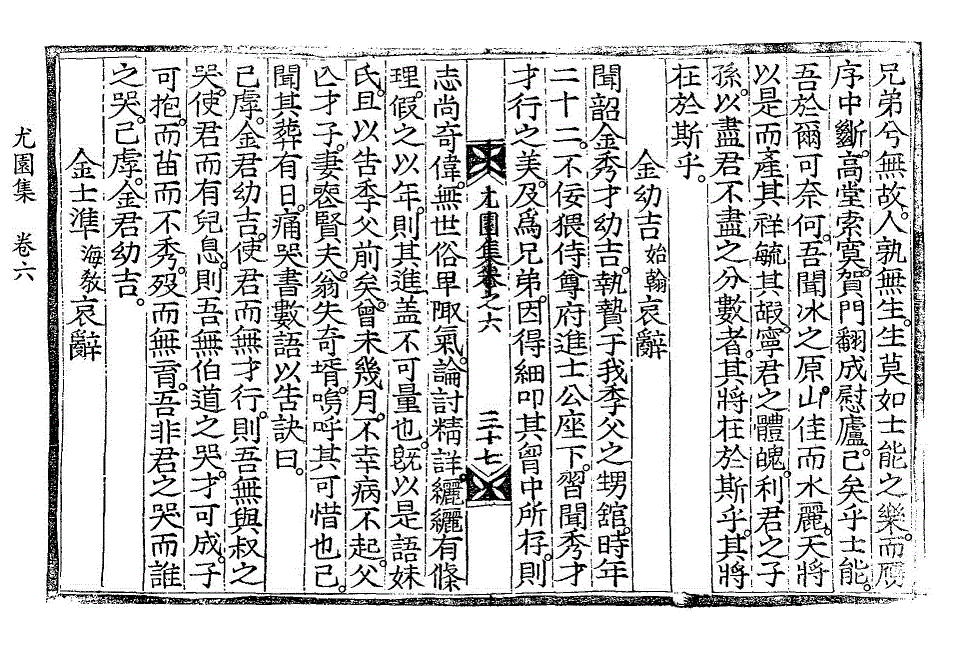 兄弟兮无故。人孰无生。生莫如士能之乐。而雁序中断。高堂索寞。贺门翻成慰庐。已矣乎士能。吾于尔可奈何。吾闻冰之原。山佳而水丽。天将以是而产其祥毓其嘏。宁君之体魄。利君之子孙。以尽君不尽之分数者。其将在于斯乎。其将在于斯乎。
兄弟兮无故。人孰无生。生莫如士能之乐。而雁序中断。高堂索寞。贺门翻成慰庐。已矣乎士能。吾于尔可奈何。吾闻冰之原。山佳而水丽。天将以是而产其祥毓其嘏。宁君之体魄。利君之子孙。以尽君不尽之分数者。其将在于斯乎。其将在于斯乎。金幼吉(始翰)哀辞
闻韶金秀才幼吉。执贽于我季父之甥馆。时年二十二。不佞猥侍尊府进士公座下。习闻秀才才行之美。及为兄弟。因得细叩其胸中所存。则志尚奇伟。无世俗卑陬气。论讨精详。纚纚有条理。假之以年。则其进盖不可量也。既以是语妹氏。且以告季父前矣。曾未几月。不幸病不起。父亡才子。妻丧贤夫。翁失奇婿。呜呼其可惜也已。闻其葬有日。痛哭书数语以告诀曰。
已虖。金君幼吉。使君而无才行。则吾无与叔之哭。使君而有儿息。则吾无伯道之哭。才可成。子可抱。而苗而不秀。殁而无育。吾非君之哭而谁之哭。已虖。金君幼吉。
金士准(海教)哀辞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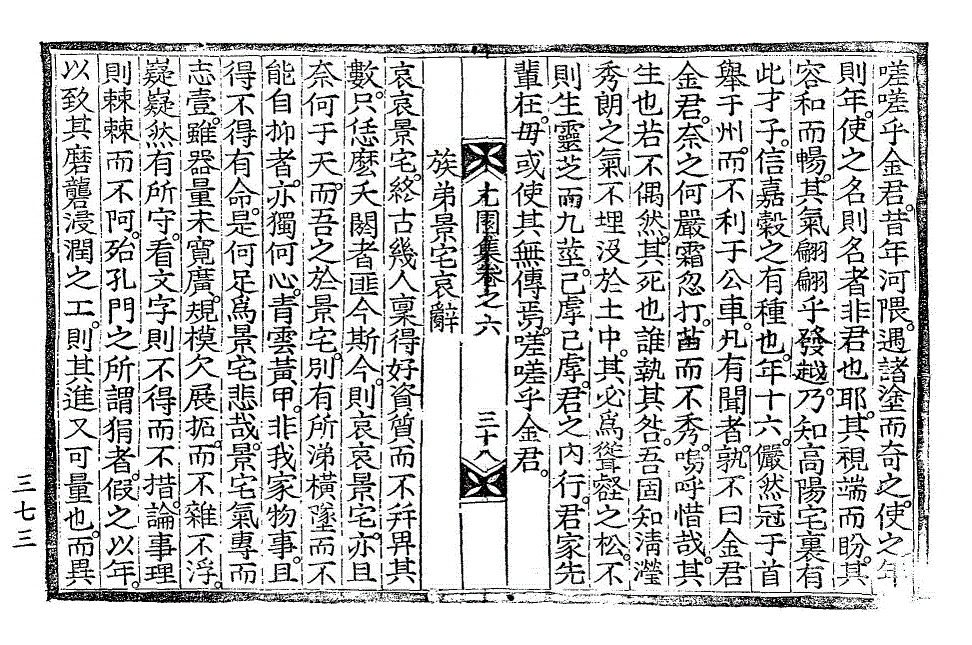 嗟嗟乎金君。昔年河隈。遇诸涂而奇之。使之年则年。使之名则名者非君也耶。其视端而盼。其容和而畅。其气翩翩乎发越。乃知高阳宅里有此才子。信嘉谷之有种也。年十六。俨然冠于首举于州。而不利于公车。凡有闻者。孰不曰金君金君。奈之何严霜忽打。苗而不秀。呜呼惜哉。其生也若不偶然。其死也谁执其咎。吾固知清滢秀朗之气不埋没于土中。其必为耸壑之松。不则生灵芝而九茎。已虖已虖。君之内行。君家先辈在。毋或使其无传焉。嗟嗟乎金君。
嗟嗟乎金君。昔年河隈。遇诸涂而奇之。使之年则年。使之名则名者非君也耶。其视端而盼。其容和而畅。其气翩翩乎发越。乃知高阳宅里有此才子。信嘉谷之有种也。年十六。俨然冠于首举于州。而不利于公车。凡有闻者。孰不曰金君金君。奈之何严霜忽打。苗而不秀。呜呼惜哉。其生也若不偶然。其死也谁执其咎。吾固知清滢秀朗之气不埋没于土中。其必为耸壑之松。不则生灵芝而九茎。已虖已虖。君之内行。君家先辈在。毋或使其无传焉。嗟嗟乎金君。族弟景宅哀辞
哀哀景宅。终古几人禀得好资质而不并畀其数。只恁么夭阏者匪今斯今。则哀哀景宅。亦且奈何于天。而吾之于景宅。别有所涕横坠而不能自抑者。亦独何心。青云黄甲。非我家物事。且得不得有命。是何足为景宅悲哉。景宅气专而志壹。虽器量未宽广。规模欠展拓。而不杂不浮。嶷嶷然有所守。看文字则不得而不措。论事理则棘棘而不阿。殆孔门之所谓狷者。假之以年。以致其磨砻浸润之工。则其进又可量也。而异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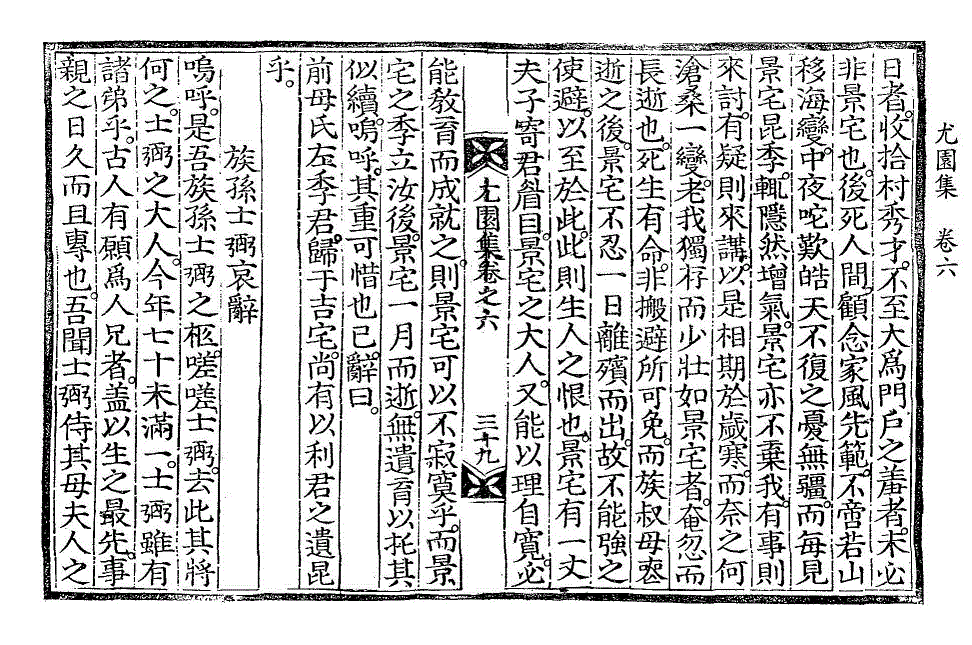 日者。收拾村秀才。不至大为门户之羞者。未必非景宅也。后死人间。顾念家风先范。不啻若山移海变。中夜咜叹皓天不复之忧无疆。而每见景宅昆季。辄隐然增气。景宅亦不弃我。有事则来讨。有疑则来讲。以是相期于岁寒。而奈之何沧桑一变。老我独存而少壮如景宅者。奄忽而长逝也。死生有命。非搬避所可免。而族叔母丧逝之后。景宅不忍一日离殡而出。故不能强之使避。以至于此。此则生人之恨也。景宅有一丈夫子寄君眉目。景宅之大人。又能以理自宽。必能教育而成就之。则景宅可以不寂寞乎。而景宅之季立汝后。景宅一月而逝。无遗育以托其似续。呜呼。其重可惜也已。辞曰。
日者。收拾村秀才。不至大为门户之羞者。未必非景宅也。后死人间。顾念家风先范。不啻若山移海变。中夜咜叹皓天不复之忧无疆。而每见景宅昆季。辄隐然增气。景宅亦不弃我。有事则来讨。有疑则来讲。以是相期于岁寒。而奈之何沧桑一变。老我独存而少壮如景宅者。奄忽而长逝也。死生有命。非搬避所可免。而族叔母丧逝之后。景宅不忍一日离殡而出。故不能强之使避。以至于此。此则生人之恨也。景宅有一丈夫子寄君眉目。景宅之大人。又能以理自宽。必能教育而成就之。则景宅可以不寂寞乎。而景宅之季立汝后。景宅一月而逝。无遗育以托其似续。呜呼。其重可惜也已。辞曰。前母氏左季君。归于吉宅。尚有以利君之遗昆乎。
族孙士弼哀辞
呜呼。是吾族孙士弼之柩。嗟嗟士弼。去此其将何之。士弼之大人。今年七十未满一。士弼虽有诸弟乎。古人有愿为人兄者。盖以生之最先。事亲之日久而且专也。吾闻士弼侍其母夫人之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3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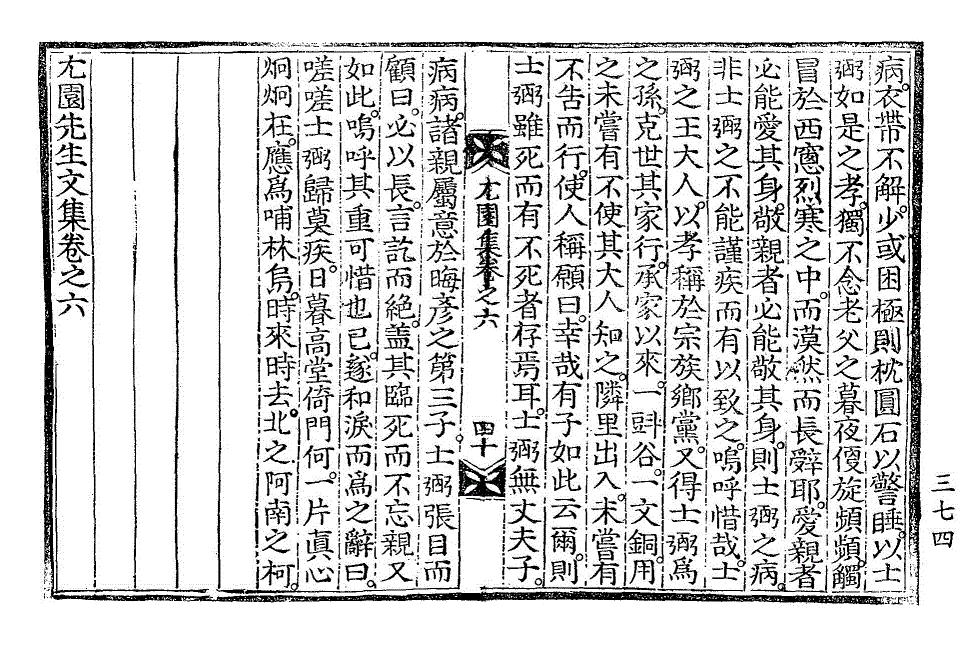 病。衣带不解。少或困极则枕圆石以警睡。以士弼如是之孝。独不念老父之暮夜便旋频频。触冒于西窗烈寒之中。而漠然而长辞耶。爱亲者必能爱其身。敬亲者必能敬其身。则士弼之病。非士弼之不能谨疾而有以致之。呜呼惜哉。士弼之王大人。以孝称于宗族乡党。又得士弼为之孙。克世其家行。承家以来。一㪷谷。一文铜。用之未尝有不使其大人知之。邻里出入。未尝有不告而行。使人称愿曰。幸哉有子如此云尔。则士弼虽死而有不死者存焉耳。士弼无丈夫子。病病。诸亲属意于晦彦之第三子。士弼张目而顾曰。必以长。言讫而绝。盖其临死而不忘亲又如此。呜呼其重可惜也已。遂和泪而为之辞曰。
病。衣带不解。少或困极则枕圆石以警睡。以士弼如是之孝。独不念老父之暮夜便旋频频。触冒于西窗烈寒之中。而漠然而长辞耶。爱亲者必能爱其身。敬亲者必能敬其身。则士弼之病。非士弼之不能谨疾而有以致之。呜呼惜哉。士弼之王大人。以孝称于宗族乡党。又得士弼为之孙。克世其家行。承家以来。一㪷谷。一文铜。用之未尝有不使其大人知之。邻里出入。未尝有不告而行。使人称愿曰。幸哉有子如此云尔。则士弼虽死而有不死者存焉耳。士弼无丈夫子。病病。诸亲属意于晦彦之第三子。士弼张目而顾曰。必以长。言讫而绝。盖其临死而不忘亲又如此。呜呼其重可惜也已。遂和泪而为之辞曰。嗟嗟士弼归莫疾。日暮高堂倚门何。一片真心炯炯在。应为哺林乌。时来时去。北之阿南之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