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讲议
讲议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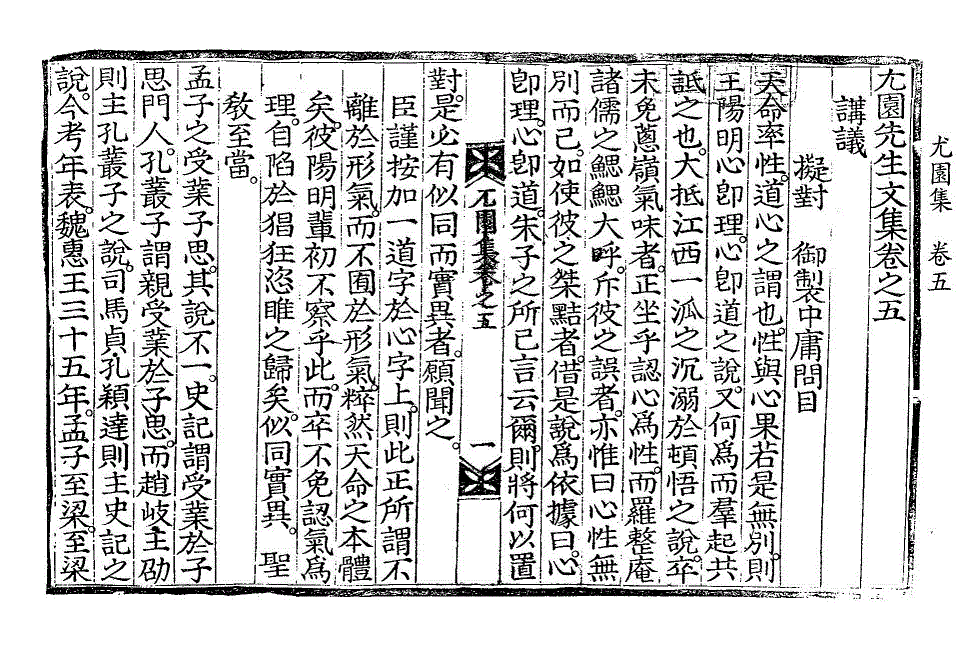 拟对 御制中庸问目
拟对 御制中庸问目天命率性。道心之谓也。性与心果若是无别。则王阳明心即理。心即道之说。又何为而群起共诋之也。大抵江西一派之沉溺于顿悟之说。卒未免葱岭气味者。正坐乎认心为性。而罗整庵诸儒之鳃鳃大呼。斥彼之误者。亦惟曰心性无别而已。如使彼之桀黠者。借是说为依据曰。心即理。心即道。朱子之所已言云尔。则将何以置对。是必有似同而实异者。愿闻之。
臣谨按加一道字于心字上。则此正所谓不离于形气。而不囿于形气。粹然天命之本体矣。彼阳明辈初不察乎此。而卒不免认气为理。自陷于猖狂恣睢之归矣。似同实异。 圣教至当。
孟子之受业子思。其说不一。史记谓受业于子思门人。孔丛子谓亲受业于子思。而赵岐,王劭则主孔丛子之说。司马贞,孔颖达则主史记之说。今考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至梁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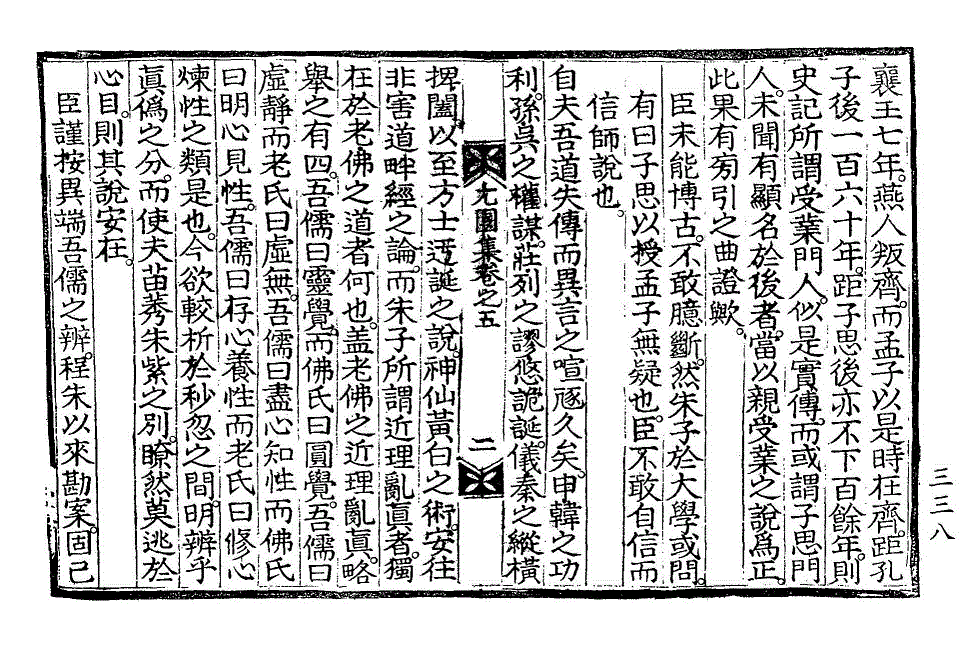 襄王七年。燕人叛齐。而孟子以是时在齐。距孔子后一百六十年。距子思后亦不下百馀年。则史记所谓受业门人。似是实传。而或谓子思门人。未闻有显名于后者。当以亲受业之说为正。此果有旁引之曲證欤。
襄王七年。燕人叛齐。而孟子以是时在齐。距孔子后一百六十年。距子思后亦不下百馀年。则史记所谓受业门人。似是实传。而或谓子思门人。未闻有显名于后者。当以亲受业之说为正。此果有旁引之曲證欤。臣未能博古。不敢臆断。然朱子于大学或问。有曰子思以授孟子无疑也。臣不敢自信而信师说也。
自夫吾道失传而异言之喧豗久矣。申,韩之功利。孙,吴之权谋。庄,列之谬,悠诡诞。仪秦之纵横捭阖。以至方士迂诞之说。神仙黄白之术。安往非害道畔经之论。而朱子所谓近理乱真者。独在于老佛之道者何也。盖老佛之近理乱真。略举之有四。吾儒曰灵觉。而佛氏曰圆觉。吾儒曰虚静而老氏曰虚无。吾儒曰尽心知性而佛氏曰明心见性。吾儒曰存心养性而老氏曰修心炼性之类是也。今欲较析于秒忽之间。明辨乎真伪之分。而使夫苗莠朱紫之别。瞭然莫逃于心目。则其说安在。
臣谨按异端吾儒之辨。程朱以来勘案。固已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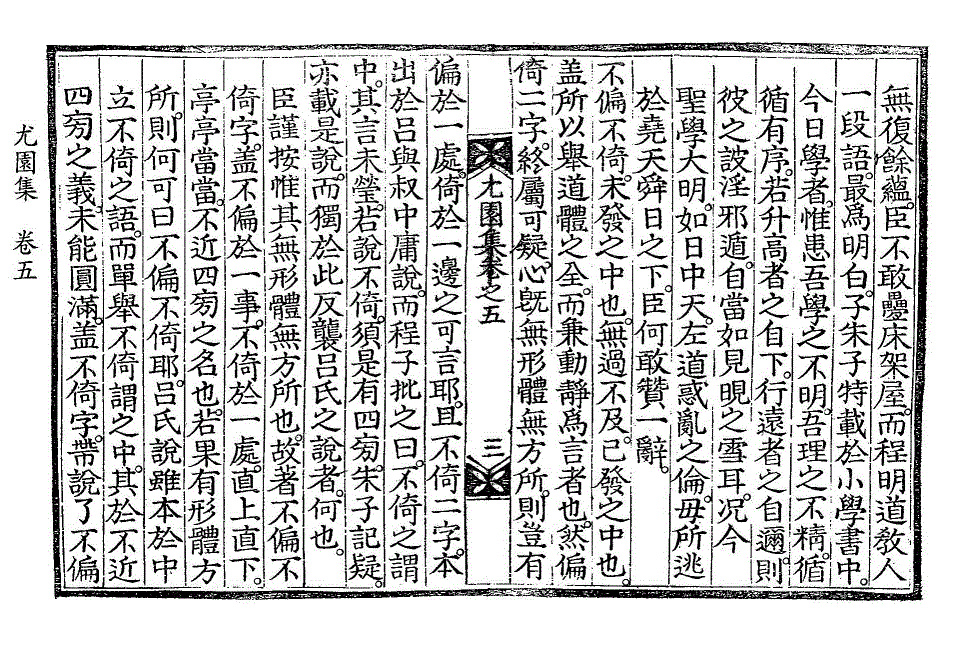 无复馀蕴。臣不敢叠床架屋。而程明道教人一段语。最为明白。子朱子特载于小学书中。今日学者。惟患吾学之不明。吾理之不精。循循有序。若升高者之自下。行远者之自迩。则彼之诐淫邪遁。自当如见晛之雪耳。况今 圣学大明。如日中天。左道惑乱之伦。毋所逃于尧天舜日之下。臣何敢赞一辞。
无复馀蕴。臣不敢叠床架屋。而程明道教人一段语。最为明白。子朱子特载于小学书中。今日学者。惟患吾学之不明。吾理之不精。循循有序。若升高者之自下。行远者之自迩。则彼之诐淫邪遁。自当如见晛之雪耳。况今 圣学大明。如日中天。左道惑乱之伦。毋所逃于尧天舜日之下。臣何敢赞一辞。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也。无过不及。已发之中也。盖所以举道体之全。而兼动静为言者也。然偏倚二字。终属可疑。心既无形体无方所。则岂有偏于一处。倚于一边之可言耶。且不倚二字。本出于吕与叔中庸说。而程子批之曰。不倚之谓中。其言未莹。若说不倚。须是有四旁。朱子记疑。亦载是说。而独于此反袭吕氏之说者。何也。
臣谨按惟其无形体无方所也。故著不偏不倚字。盖不偏于一事。不倚于一处。直上直下。亭亭当当。不近四旁之名也。若果有形体方所。则何可曰不偏不倚耶。吕氏说虽本于中立不倚之语。而单举不倚谓之中。其于不近四旁之义。未能圆满。盖不倚字。带说了不偏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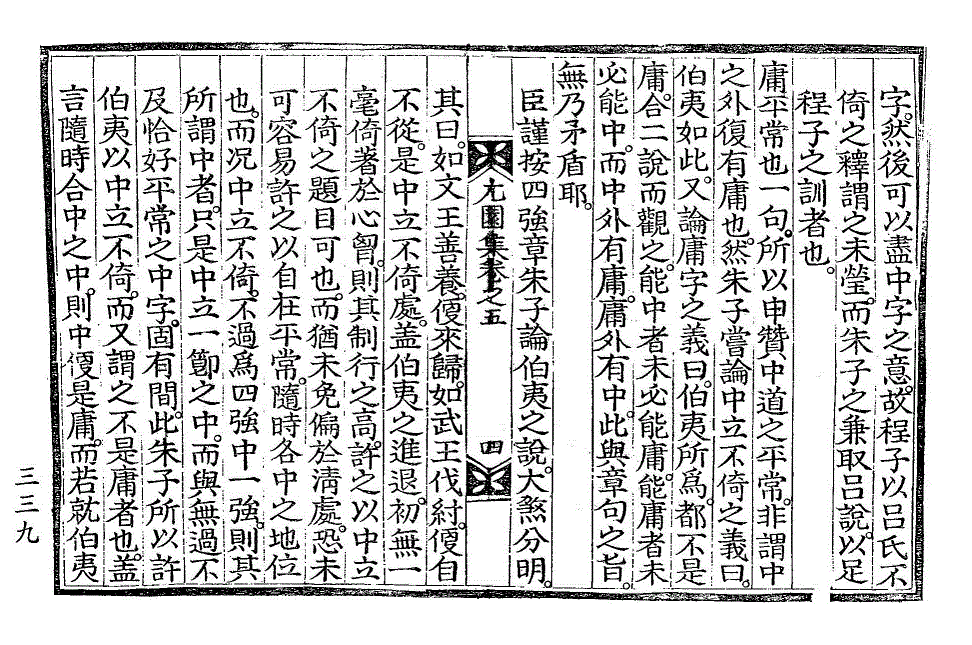 字。然后可以尽中字之意。故程子以吕氏不倚之释谓之未莹。而朱子之兼取吕说。以足程子之训者也。
字。然后可以尽中字之意。故程子以吕氏不倚之释谓之未莹。而朱子之兼取吕说。以足程子之训者也。庸平常也一句。所以申赞中道之平常。非谓中之外复有庸也。然朱子尝论中立不倚之义曰。伯夷如此。又论庸字之义曰。伯夷所为。都不是庸。合二说而观之。能中者未必能庸。能庸者未必能中。而中外有庸。庸外有中。此与章句之旨。无乃矛盾耶。
臣谨按四强章朱子论伯夷之说。大煞分明。其曰。如文王善养。便来归。如武王伐纣。便自不从。是中立不倚处。盖伯夷之进退。初无一毫倚著于心胸。则其制行之高。许之以中立不倚之题目可也。而犹未免偏于清处。恐未可容易许之以自在平常。随时各中之地位也。而况中立不倚。不过为四强中一强。则其所谓中者。只是中立一节之中。而与无过不及恰好平常之中字。固有间。此朱子所以许伯夷以中立不倚。而又谓之不是庸者也。盖言随时合中之中。则中便是庸。而若就伯夷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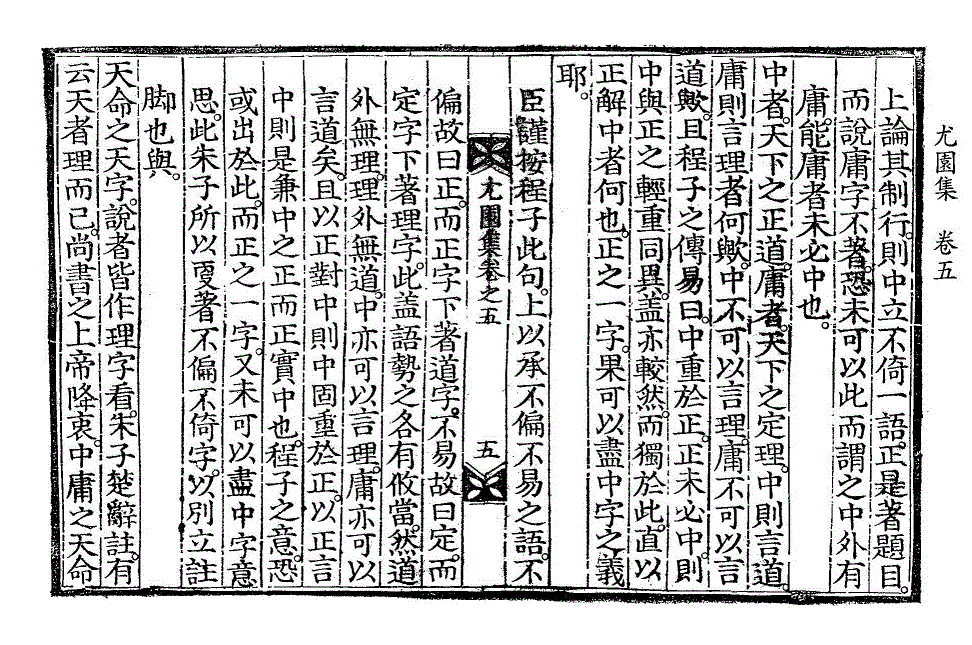 上论其制行。则中立不倚一语。正是著题目。而说庸字不著。恐未可以此而谓之中外有庸。能庸者未必中也。
上论其制行。则中立不倚一语。正是著题目。而说庸字不著。恐未可以此而谓之中外有庸。能庸者未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则言道。庸则言理者何欤。中不可以言理。庸不可以言道欤。且程子之传易曰。中重于正。正未必中。则中与正之轻重同异。盖亦较然。而独于此。直以正解中者何也。正之一字。果可以尽中字之义耶。
臣谨按程子此句。上以承不偏不易之语。不偏故曰正。而正字下著道字。不易故曰定。而定字下著理字。此盖语势之各有攸当。然道外无理。理外无道。中亦可以言理。庸亦可以言道矣。且以正对中则中固重于正。以正言中则是兼中之正而正实中也。程子之意。恐或出于此。而正之一字。又未可以尽中字意思。此朱子所以更著不偏不倚字。以别立注脚也与。
天命之天字。说者皆作理字看。朱子楚辞注。有云天者理而已。尚书之上帝降衷。中庸之天命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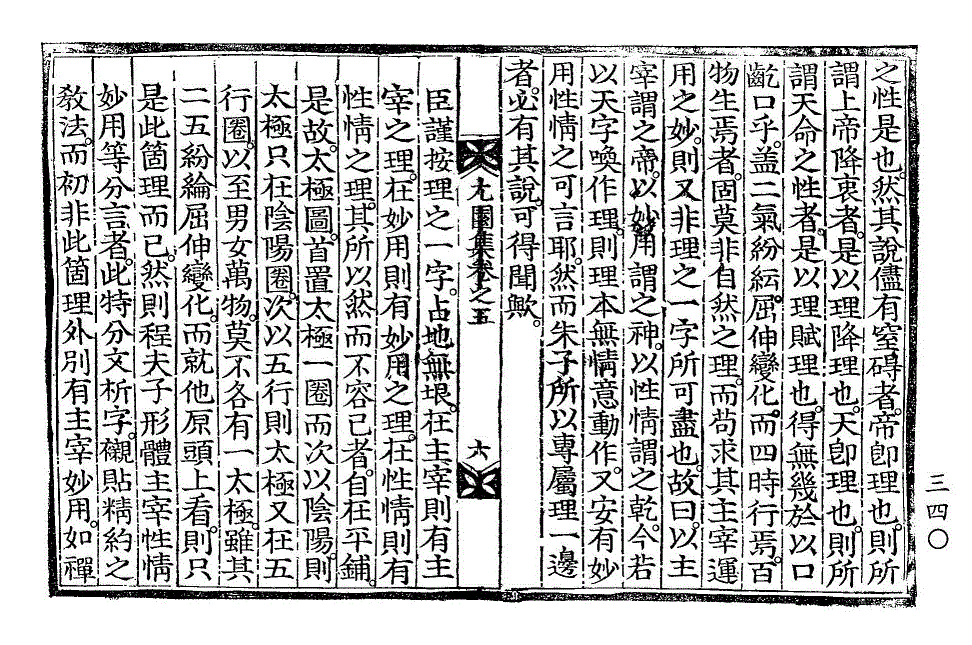 之性是也。然其说尽有窒碍者。帝即理也。则所谓上帝降衷者。是以理降理也。天即理也。则所谓天命之性者。是以理赋理也。得无几于以口龁口乎。盖二气纷纭。屈伸变化。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者。固莫非自然之理。而苟求其主宰运用之妙。则又非理之一字所可尽也。故曰。以主宰谓之帝。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今若以天字唤作理。则理本无情意动作。又安有妙用性情之可言耶。然而朱子所以专属理一边者。必有其说。可得闻欤。
之性是也。然其说尽有窒碍者。帝即理也。则所谓上帝降衷者。是以理降理也。天即理也。则所谓天命之性者。是以理赋理也。得无几于以口龁口乎。盖二气纷纭。屈伸变化。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者。固莫非自然之理。而苟求其主宰运用之妙。则又非理之一字所可尽也。故曰。以主宰谓之帝。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乾。今若以天字唤作理。则理本无情意动作。又安有妙用性情之可言耶。然而朱子所以专属理一边者。必有其说。可得闻欤。臣谨按理之一字。占地无垠。在主宰则有主宰之理。在妙用则有妙用之理。在性情则有性情之理。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自在平铺。是故。太极图。首置太极一圈而次以阴阳。则太极只在阴阳圈。次以五行则太极又在五行圈。以至男女万物。莫不各有一太极。虽其二五纷纶屈伸变化。而就他原头上看。则只是此个理而已。然则程夫子形体主宰性情妙用等分言者。此特分文析字。衬贴精约之教法。而初非此个理外别有主宰妙用。如禅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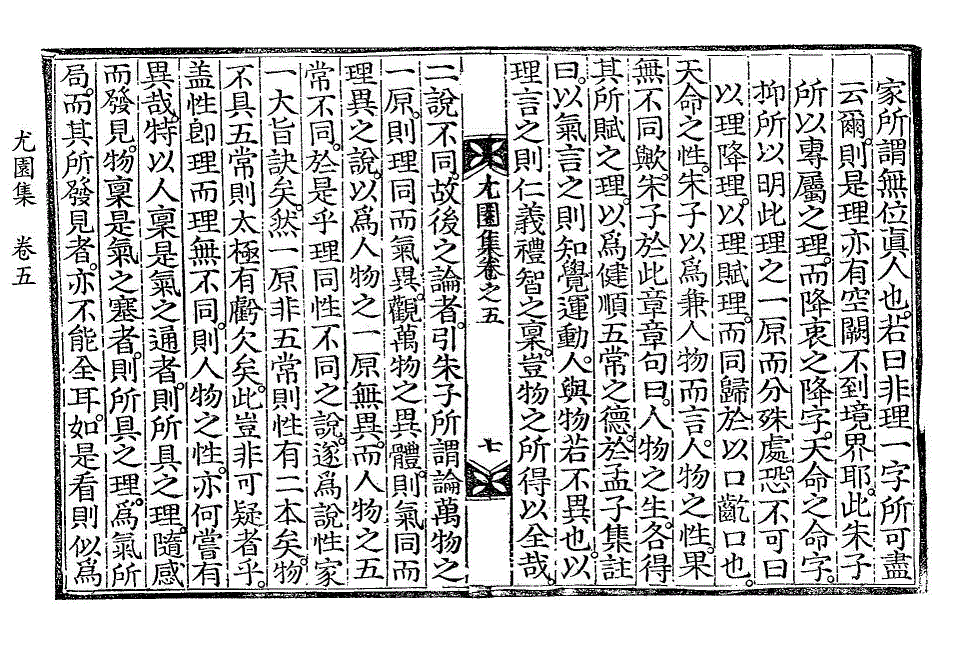 家所谓无位真人也。若曰非理一字所可尽云尔。则是理亦有空阙不到境界耶。此朱子所以专属之理。而降衷之降字。天命之命字。抑所以明此理之一原而分殊处。恐不可曰以理降理。以理赋理。而同归于以口龁口也。
家所谓无位真人也。若曰非理一字所可尽云尔。则是理亦有空阙不到境界耶。此朱子所以专属之理。而降衷之降字。天命之命字。抑所以明此理之一原而分殊处。恐不可曰以理降理。以理赋理。而同归于以口龁口也。天命之性。朱子以为兼人物而言。人物之性。果无不同欤。朱子于此章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于孟子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以全哉。二说不同。故后之论者。引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同而理异之说。以为人物之一原无异。而人物之五常不同。于是乎理同性不同之说。遂为说性家一大旨诀矣。然一原非五常则性有二本矣。物不具五常则太极有亏欠矣。此岂非可疑者乎。盖性即理而理无不同。则人物之性。亦何尝有异哉。特以人禀是气之通者。则所具之理。随感而发见。物禀是气之塞者。则所具之理。为气所局。而其所发见者。亦不能全耳。如是看则似为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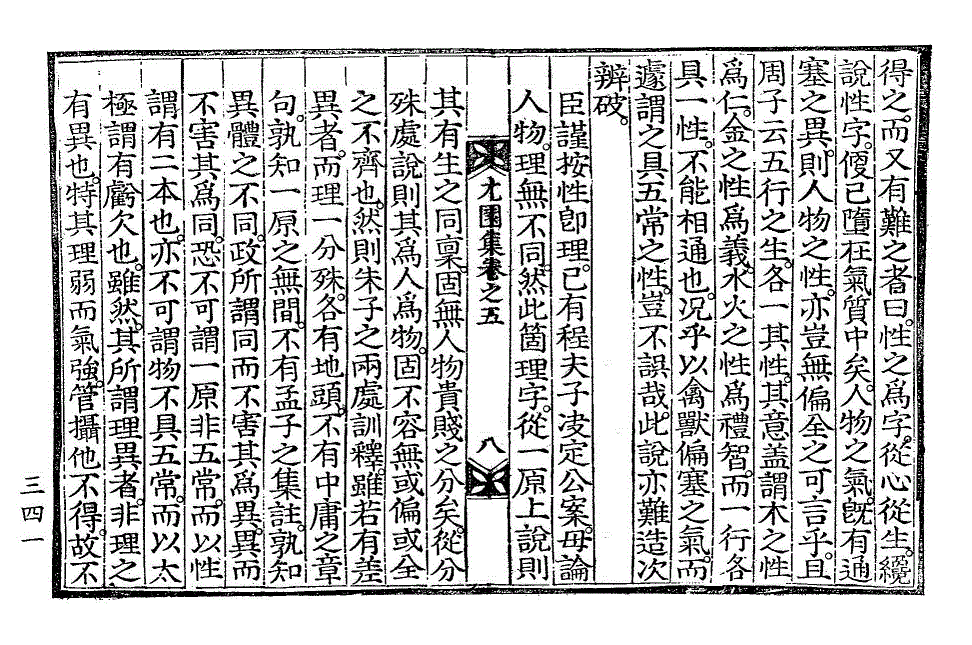 得之。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从心从生。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人物之气。既有通塞之异。则人物之性。亦岂无偏全之可言乎。且周子云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金之性为义。水火之性为礼智。而一行各具一性。不能相通也。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岂不误哉。此说亦难造次辨破。
得之。而又有难之者曰。性之为字。从心从生。才说性字。便已堕在气质中矣。人物之气。既有通塞之异。则人物之性。亦岂无偏全之可言乎。且周子云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意盖谓木之性为仁。金之性为义。水火之性为礼智。而一行各具一性。不能相通也。况乎以禽兽偏塞之气。而遽谓之具五常之性。岂不误哉。此说亦难造次辨破。臣谨按性即理。已有程夫子决定公案。毋论人物。理无不同。然此个理字。从一原上说则其有生之同禀。固无人物贵贱之分矣。从分殊处说则其为人为物。固不容无或偏或全之不齐也。然则朱子之两处训释。虽若有差异者。而理一分殊。各有地头。不有中庸之章句。孰知一原之无间。不有孟子之集注。孰知异体之不同。政所谓同而不害其为异。异而不害其为同。恐不可谓一原非五常。而以性谓有二本也。亦不可谓物不具五常。而以太极谓有亏欠也。虽然。其所谓理异者。非理之有异也。特其理弱而气强。管摄他不得。故不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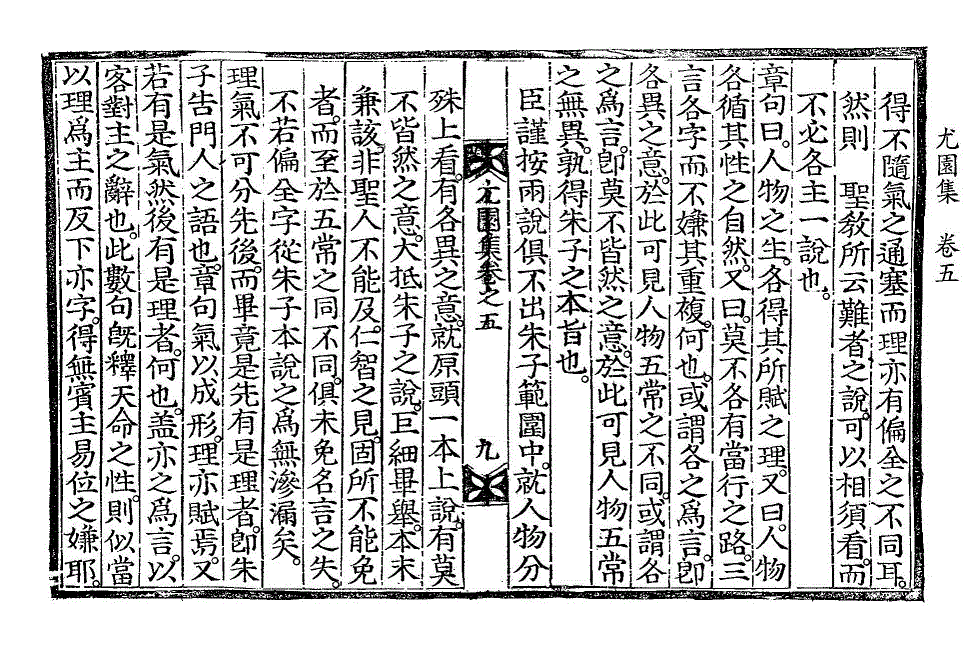 得不随气之通塞而理亦有偏全之不同耳。然则 圣教所云难者之说。可以相须看。而不必各主一说也。
得不随气之通塞而理亦有偏全之不同耳。然则 圣教所云难者之说。可以相须看。而不必各主一说也。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又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又曰。莫不各有当行之路。三言各字而不嫌其重复。何也。或谓各之为言。即各异之意。于此可见人物五常之不同。或谓各之为言。即莫不皆然之意。于此可见人物五常之无异。孰得朱子之本旨也。
臣谨按两说俱不出朱子范围中。就人物分殊上看。有各异之意。就原头一本上说。有莫不皆然之意。大抵朱子之说。巨细毕举。本末兼该。非圣人不能及。仁智之见。固所不能免者。而至于五常之同不同。俱未免名言之失。不若偏全字从朱子本说之为无渗漏矣。
理气不可分先后。而毕竟是先有是理者。即朱子告门人之语也。章句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又若有是气然后有是理者。何也。盖亦之为言。以客对主之辞也。此数句既释天命之性。则似当以理为主而反下亦字。得无宾主易位之嫌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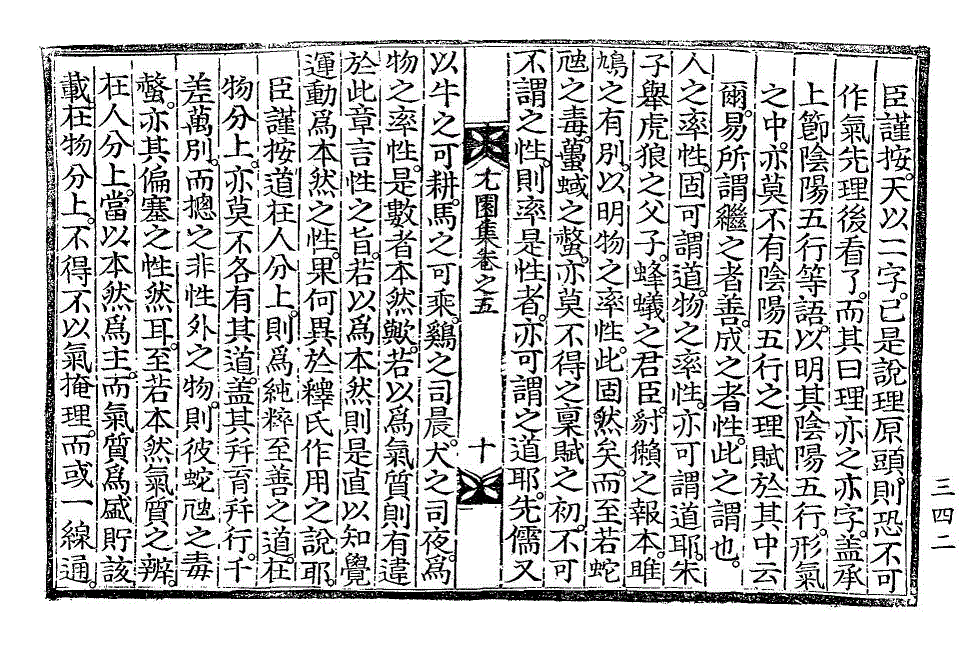 臣谨按。天以二字。已是说理原头。则恐不可作气先理后看了。而其曰理亦之亦字。盖承上节阴阳五行等语。以明其阴阳五行。形气之中。亦莫不有阴阳五行之理赋于其中云尔。易所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之谓也。
臣谨按。天以二字。已是说理原头。则恐不可作气先理后看了。而其曰理亦之亦字。盖承上节阴阳五行等语。以明其阴阳五行。形气之中。亦莫不有阴阳五行之理赋于其中云尔。易所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此之谓也。人之率性。固可谓道。物之率性。亦可谓道耶。朱子举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以明物之率性。此固然矣。而至若蛇虺之毒。虿蜮之螫。亦莫不得之禀赋之初。不可不谓之性。则率是性者。亦可谓之道耶。先儒又以牛之可耕。马之可乘。鸡之司晨。犬之司夜。为物之率性。是数者本然欤。若以为气质则有违于此章言性之旨。若以为本然则是直以知觉运动为本然之性。果何异于释氏作用之说耶。
臣谨按道在人分上。则为纯粹至善之道。在物分上。亦莫不各有其道。盖其并育并行。千差万别。而总之非性外之物。则彼蛇虺之毒螫。亦其偏塞之性然耳。至若本然气质之辨。在人分上。当以本然为主。而气质为盛贮该载。在物分上。不得不以气掩理。而或一线通。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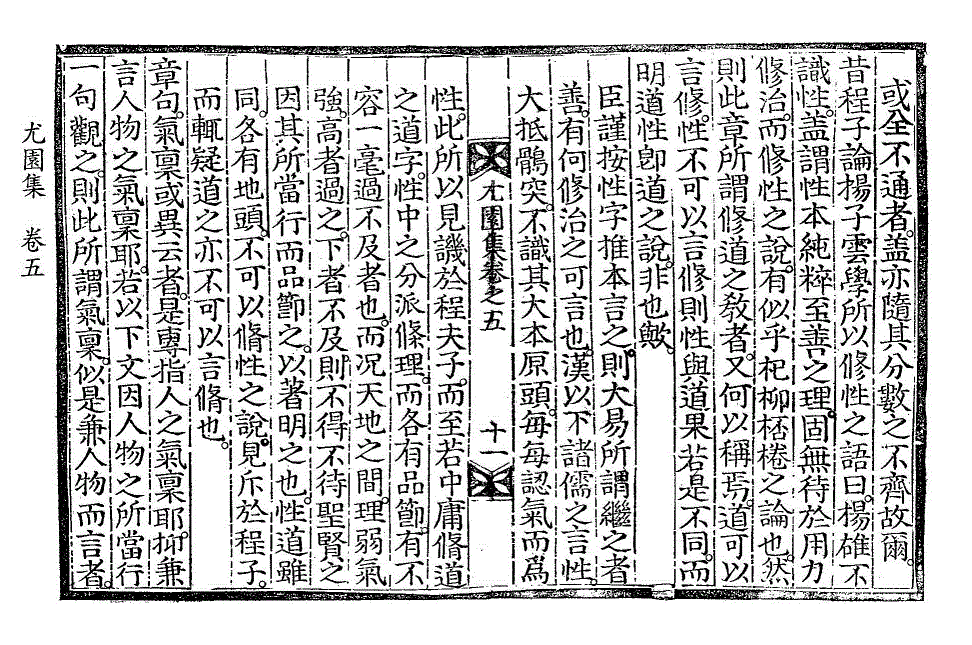 或全不通者。盖亦随其分数之不齐故尔。
或全不通者。盖亦随其分数之不齐故尔。昔程子论扬子云学所以修性之语曰。杨雄不识性。盖谓性本纯粹至善之理。固无待于用力修治。而修性之说。有似乎杞柳杯棬之论也。然则此章所谓修道之教者。又何以称焉。道可以言修。性不可以言修则性与道果若是不同。而明道性即道之说。非也欤。
臣谨按性字推本言之。则大易所谓继之者善。有何修治之可言也。汉以不诸儒之言性。大抵鹘突。不识其大本原头。每每认气而为性。此所以见讥于程夫子。而至若中庸脩道之道字。性中之分派条理。而各有品节。有不容一毫过不及者也。而况天地之间。理弱气强。高者过之。下者不及。则不得不待圣贤之因其所当行而品节之。以著明之也。性道虽同。各有地头。不可以脩性之说。见斥于程子。而辄疑道之亦不可以言脩也。
章句。气禀或异云者。是专指人之气禀耶。抑兼言人物之气禀耶。若以下文因人物之所当行一句观之。则此所谓气禀。似是兼人物而言者。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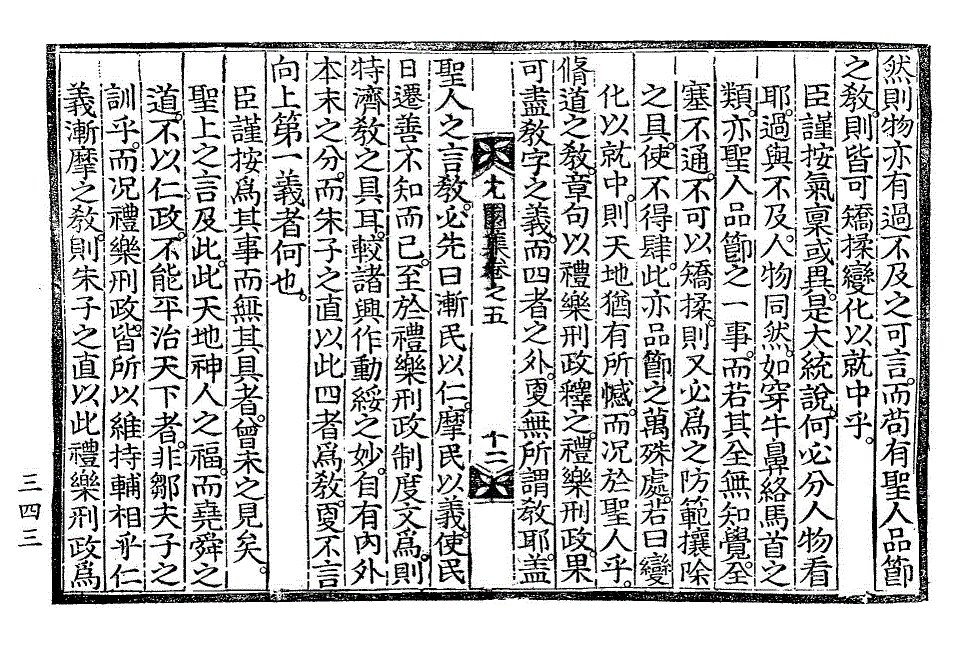 然则物亦有过不及之可言。而苟有圣人品节之教。则皆可矫揉变化以就中乎。
然则物亦有过不及之可言。而苟有圣人品节之教。则皆可矫揉变化以就中乎。臣谨按气禀或异。是大统说。何必分人物看耶。过与不及。人物同然。如穿牛鼻络马首之类。亦圣人品节之一事。而若其全无知觉。全塞不通。不可以矫揉。则又必为之防范攘除之具。使不得肆。此亦品节之万殊处。若曰变化以就中。则天地犹有所憾。而况于圣人乎。
脩道之教。章句以礼乐刑政释之。礼乐刑政。果可尽教字之义。而四者之外。更无所谓教耶。盖圣人之言教。必先曰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日迁善不知而已。至于礼乐刑政制度文为。则特济教之具耳。较诸兴作动绥之妙。自有内外本末之分。而朱子之直以此四者为教。更不言向上第一义者何也。
臣谨按为其事而无其具者。曾未之见矣。 圣上之言及此。此天地神人之福。而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非邹夫子之训乎。而况礼乐刑政。皆所以维持辅相乎仁义渐摩之教。则朱子之直以此礼乐刑政为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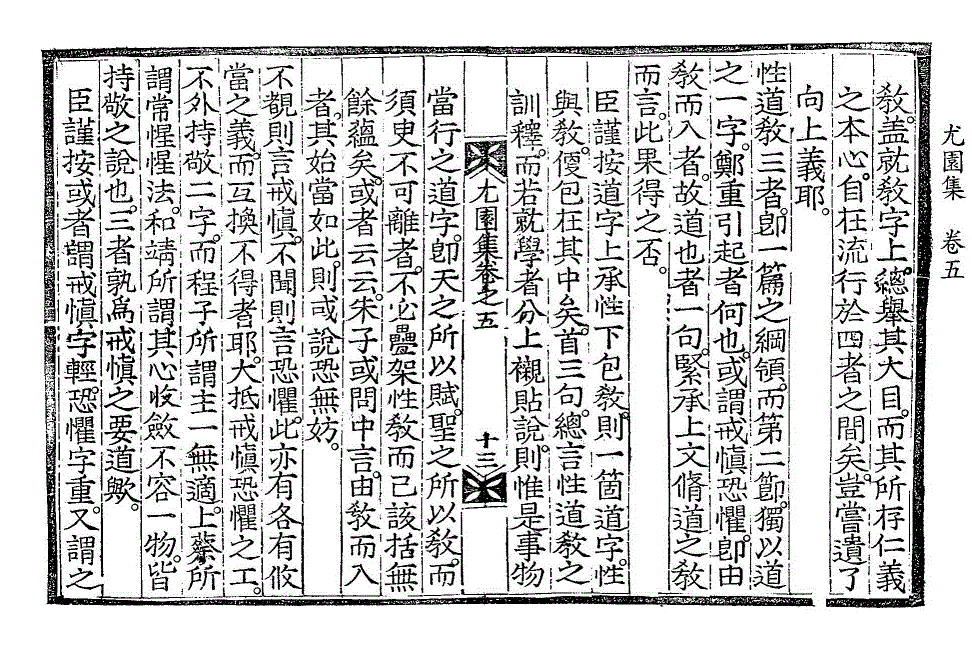 教。盖就教字上。总举其大目。而其所存仁义之本心。自在流行于四者之间矣。岂尝遗了向上义耶。
教。盖就教字上。总举其大目。而其所存仁义之本心。自在流行于四者之间矣。岂尝遗了向上义耶。性道教三者。即一篇之纲领。而第二节。独以道之一字。郑重引起者何也。或谓戒慎恐惧。即由教而入者。故道也者一句。紧承上文脩道之教而言。此果得之否。
臣谨按道字上承性下包教。则一个道字。性与教。便包在其中矣。首三句。总言性道教之训释。而若就学者分上衬贴说。则惟是事物当行之道字。即天之所以赋。圣之所以教。而须臾不可离者。不必叠架性教而已该括无馀蕴矣。或者云云。朱子或问中言。由教而入者。其始当如此。则或说恐无妨。
不睹则言戒慎。不闻则言恐惧。此亦有各有攸当之义。而互换不得者耶。大抵戒慎恐惧之工。不外持敬二字。而程子所谓主一无适。上蔡所谓常惺惺法。和靖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皆持敬之说也。三者孰为戒慎之要道欤。
臣谨按或者谓戒慎字轻。恐惧字重。又谓之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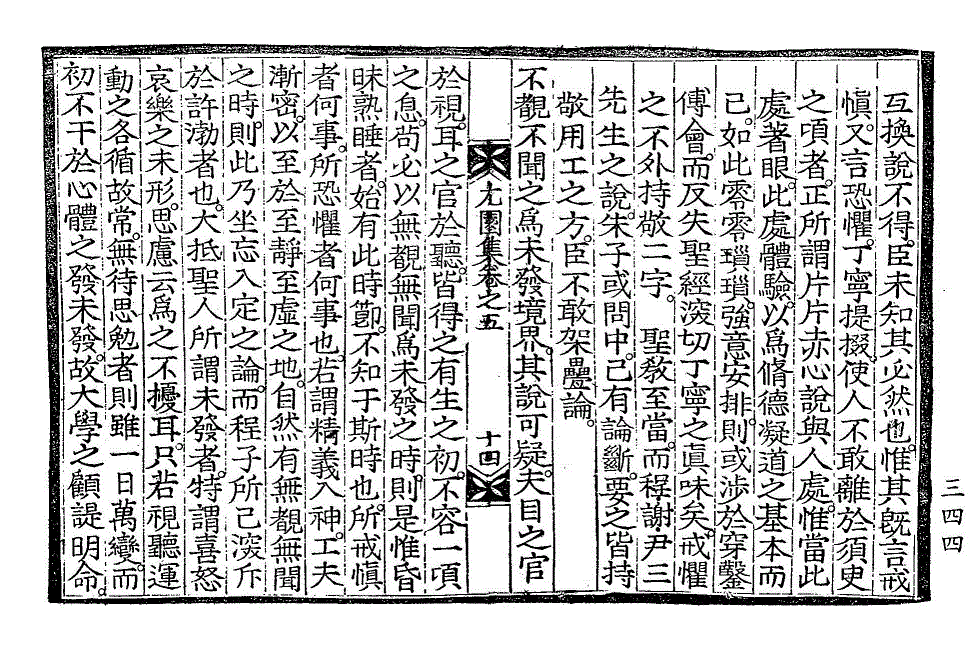 互换说不得。臣未知其必然也。惟其既言戒慎。又言恐惧。丁宁提掇。使人不敢离于须臾之顷者。正所谓片片赤心说与人处。惟当此处著眼。此处体验。以为脩德凝道之基本而已。如此零零琐琐。强意安排。则或涉于穿凿傅会。而反失圣经深切丁宁之真味矣。戒惧之不外持敬二字。 圣教至当。而程,谢,尹三先生之说。朱子或问中。已有论断。要之皆持敬用工之方。臣不敢架叠论。
互换说不得。臣未知其必然也。惟其既言戒慎。又言恐惧。丁宁提掇。使人不敢离于须臾之顷者。正所谓片片赤心说与人处。惟当此处著眼。此处体验。以为脩德凝道之基本而已。如此零零琐琐。强意安排。则或涉于穿凿傅会。而反失圣经深切丁宁之真味矣。戒惧之不外持敬二字。 圣教至当。而程,谢,尹三先生之说。朱子或问中。已有论断。要之皆持敬用工之方。臣不敢架叠论。不睹不闻之为未发境界。其说可疑。夫目之官于视。耳之官于听。皆得之有生之初。不容一顷之息。苟必以无睹无闻为未发之时。则是惟昏昧熟睡者。始有此时节。不知于斯时也。所戒慎者何事。所恐惧者何事也。若谓精义入神。工夫渐密。以至于至静至虚之地。自然有无睹无闻之时。则此乃坐忘入定之论。而程子所已深斥于许渤者也。大抵圣人所谓未发者。特谓喜怒哀乐之未形。思虑云为之不扰耳。只若视听运动之各循故常。无待思勉者则虽一日万变。而初不干于心体之发未发。故大学之顾諟明命。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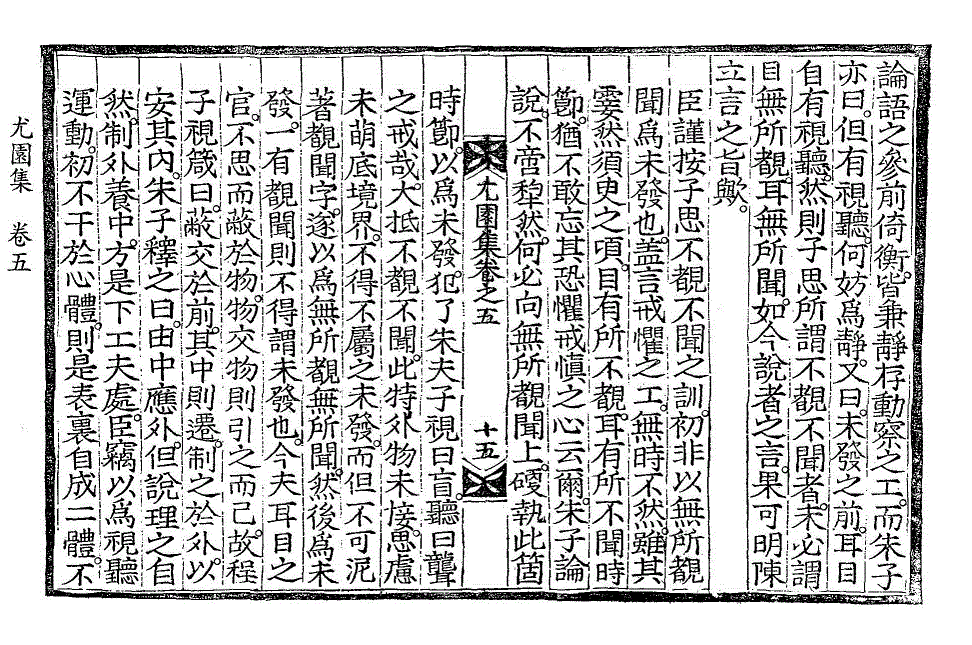 论语之参前倚衡。皆兼静存动察之工。而朱子亦曰。但有视听。何妨为静。又曰。未发之前。耳目自有视听。然则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未必谓目无所睹。耳无所闻。如今说者之言。果可明陈立言之旨欤。
论语之参前倚衡。皆兼静存动察之工。而朱子亦曰。但有视听。何妨为静。又曰。未发之前。耳目自有视听。然则子思所谓不睹不闻者。未必谓目无所睹。耳无所闻。如今说者之言。果可明陈立言之旨欤。臣谨按子思不睹不闻之训。初非以无所睹闻为未发也。盖言戒惧之工。无时不然。虽其霎然须臾之顷。目有所不睹。耳有所不闻时节。犹不敢忘其恐惧戒慎之心云尔。朱子论说。不啻犁然。何必向无所睹闻上。硬执此个时节。以为未发。犯了朱夫子视曰盲。听曰聋之戒哉。大抵不睹不闻。此特外物未接。思虑未萌底境界。不得不属之未发。而但不可泥著睹闻字。遂以为无所睹无所闻。然后为未发。一有睹闻则不得谓未发也。今夫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故程子视箴曰。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朱子释之曰。由中应外。但说理之自然。制外养中。方是下工夫处。臣窃以为视听运动。初不干于心体。则是表里自成二体。不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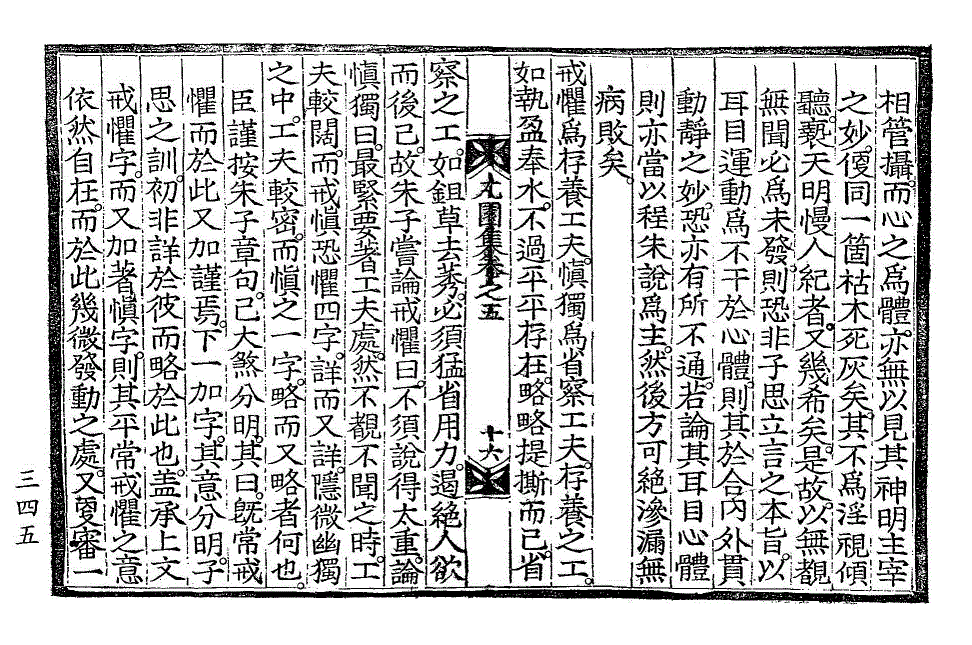 相管摄。而心之为体。亦无以见其神明主宰之妙。便同一个枯木死灰矣。其不为淫视倾听。亵天明慢人纪者。又几希矣。是故。以无睹无闻必为未发。则恐非子思立言之本旨。以耳目运动为不干于心体。则其于合内外贯动静之妙。恐亦有所不通。若论其耳目心体则亦当以程朱说为主。然后方可绝渗漏无病败矣。
相管摄。而心之为体。亦无以见其神明主宰之妙。便同一个枯木死灰矣。其不为淫视倾听。亵天明慢人纪者。又几希矣。是故。以无睹无闻必为未发。则恐非子思立言之本旨。以耳目运动为不干于心体。则其于合内外贯动静之妙。恐亦有所不通。若论其耳目心体则亦当以程朱说为主。然后方可绝渗漏无病败矣。戒惧为存养工夫。慎独为省察工夫。存养之工。如执盈奉水。不过平平存在。略略提撕而已。省察之工。如锄草去莠。必须猛省用力。遏绝人欲而后已。故朱子尝论戒惧曰。不须说得太重。论慎独曰。最紧要著工夫处。然不睹不闻之时。工夫较阔。而戒慎恐惧四字。详而又详。隐微幽独之中。工夫较密。而慎之一字。略而又略者何也。
臣谨按朱子章句。已大煞分明。其曰。既常戒惧而于此又加谨焉。下一加字。其意分明。子思之训。初非详于彼而略于此也。盖承上文戒惧字。而又加著慎字。则其平常戒惧之意依然自在。而于此几微发动之处。又更审一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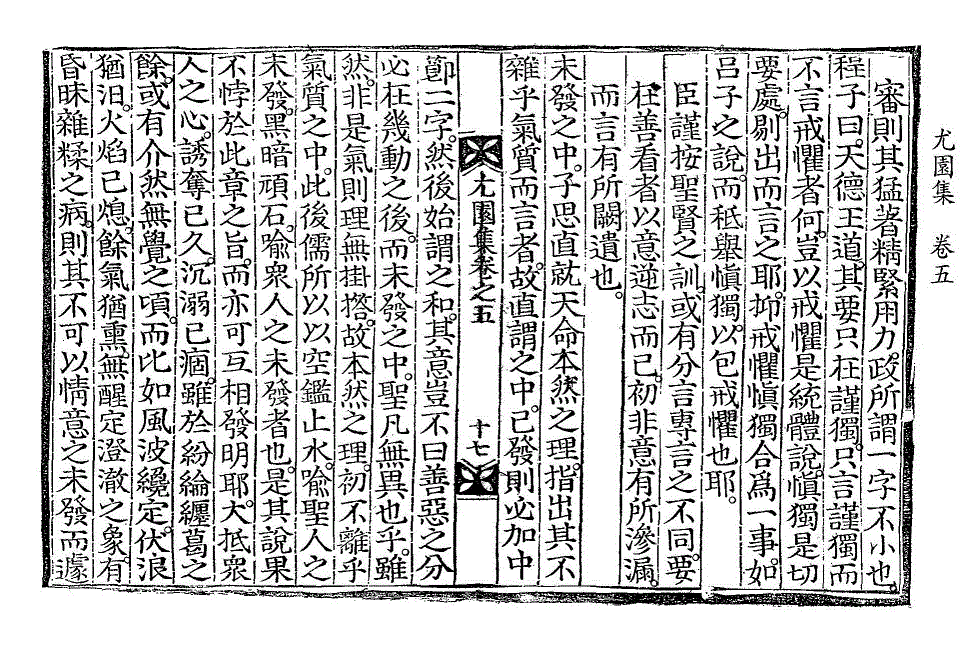 审则其猛著精紧用力。政所谓一字不小也。
审则其猛著精紧用力。政所谓一字不小也。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谨独。只言谨独而不言戒惧者何。岂以戒惧是统体说。慎独是切要处。剔出而言之耶。抑戒惧慎独合为一事。如吕子之说。而秪举慎独。以包戒惧也耶。
臣谨按圣贤之训。或有分言专言之不同。要在善看者以意逆志而已。初非意有所渗漏。而言有所阙遗也。
未发之中。子思直就天命本然之理。指出其不杂乎气质而言者。故直谓之中。已发则必加中节二字。然后始谓之和。其意岂不曰善恶之分必在几动之后。而未发之中。圣凡无异也乎。虽然。非是气则理无挂搭。故本然之理。初不离乎气质之中。此后儒所以以空鉴止水。喻圣人之未发。黑暗顽石。喻众人之未发者也。是其说果不悖于此章之旨。而亦可互相发明耶。大抵众人之心。诱夺已久。沉溺已痼。虽于纷纶缠葛之馀。或有介然无觉之顷。而比如风波才定。伏浪犹汩。火焰已熄。馀气犹熏。无醒定澄澈之象。有昏昧杂糅之病。则其不可以情意之未发而遽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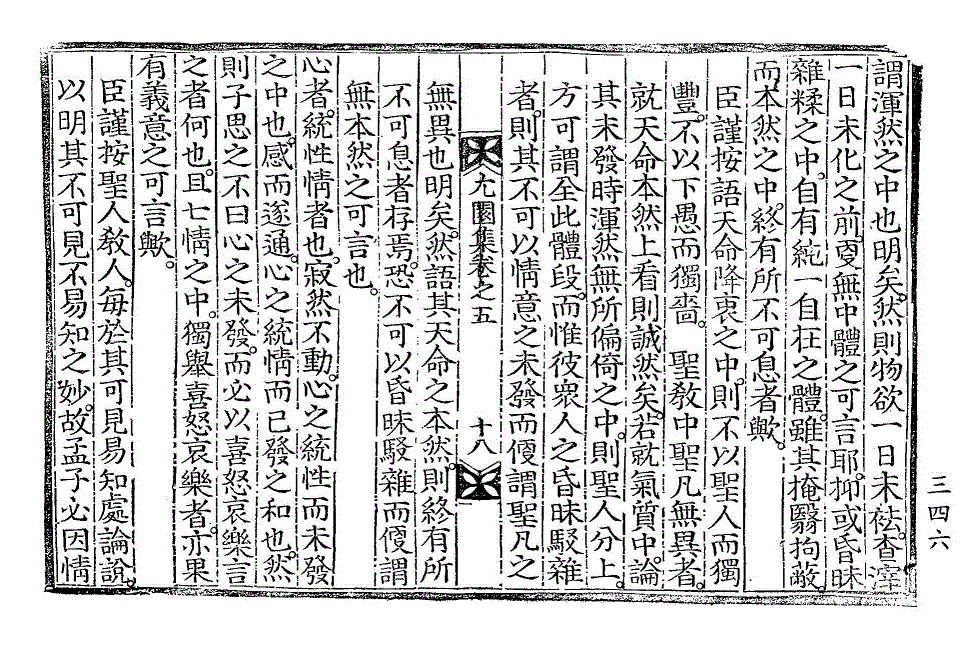 谓浑然之中也明矣。然则物欲一日未袪。查滓一日未化之前。更无中体之可言耶。抑或昏昧杂糅之中。自有纯一自在之体。虽其掩翳拘蔽。而本然之中。终有所不可息者欤。
谓浑然之中也明矣。然则物欲一日未袪。查滓一日未化之前。更无中体之可言耶。抑或昏昧杂糅之中。自有纯一自在之体。虽其掩翳拘蔽。而本然之中。终有所不可息者欤。臣谨按语天命降衷之中。则不以圣人而独丰。不以下愚而独啬。 圣教中圣凡无异者。就天命本然上看则诚然矣。若就气质中。论其未发时浑然无所偏倚之中。则圣人分上。方可谓全此体段。而惟彼众人之昏昧驳杂者。则其不可以情意之未发而便谓圣凡之无异也明矣。然语其天命之本然。则终有所不可息者存焉。恐不可以昏昧驳杂而便谓无本然之可言也。
心者。统性情者也。寂然不动。心之统性而未发之中也。感而遂通。心之统情而已发之和也。然则子思之不曰心之未发。而必以喜怒哀乐言之者何也。且七情之中。独举喜怒哀乐者。亦果有义意之可言欤。
臣谨按圣人教人。每于其可见易知处论说。以明其不可见不易知之妙。故孟子必因情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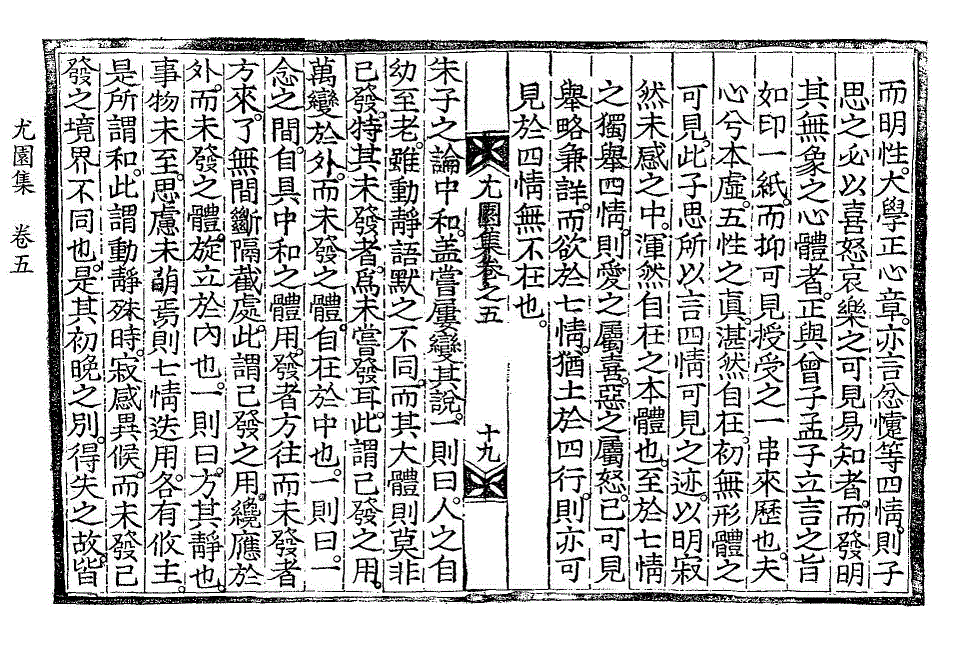 而明性。大学正心章。亦言忿懥等四情。则子思之必以喜怒哀乐之可见易知者。而发明其无象之心体者。正与曾子孟子立言之旨如印一纸。而抑可见授受之一串来历也。夫心兮本虚。五性之真。湛然自在。初无形体之可见。此子思所以言四情可见之迹。以明寂然未感之中。浑然自在之本体也。至于七情之独举四情。则爱之属喜。恶之属怒。已可见举略兼详。而欲于七情。犹土于四行。则亦可见于四情无不在也。
而明性。大学正心章。亦言忿懥等四情。则子思之必以喜怒哀乐之可见易知者。而发明其无象之心体者。正与曾子孟子立言之旨如印一纸。而抑可见授受之一串来历也。夫心兮本虚。五性之真。湛然自在。初无形体之可见。此子思所以言四情可见之迹。以明寂然未感之中。浑然自在之本体也。至于七情之独举四情。则爱之属喜。恶之属怒。已可见举略兼详。而欲于七情。犹土于四行。则亦可见于四情无不在也。朱子之论中和。盖尝屡变其说。一则曰。人之自幼至老。虽动静语默之不同。而其大体则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此谓已发之用。万变于外。而未发之体。自在于中也。一则曰。一念之间。自具中和之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此谓已发之用。才应于外。而未发之体。旋立于内也。一则曰。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是所谓和。此谓动静殊时。寂感异候。而未发已发之境界不同也。是其初晚之别。得失之故。皆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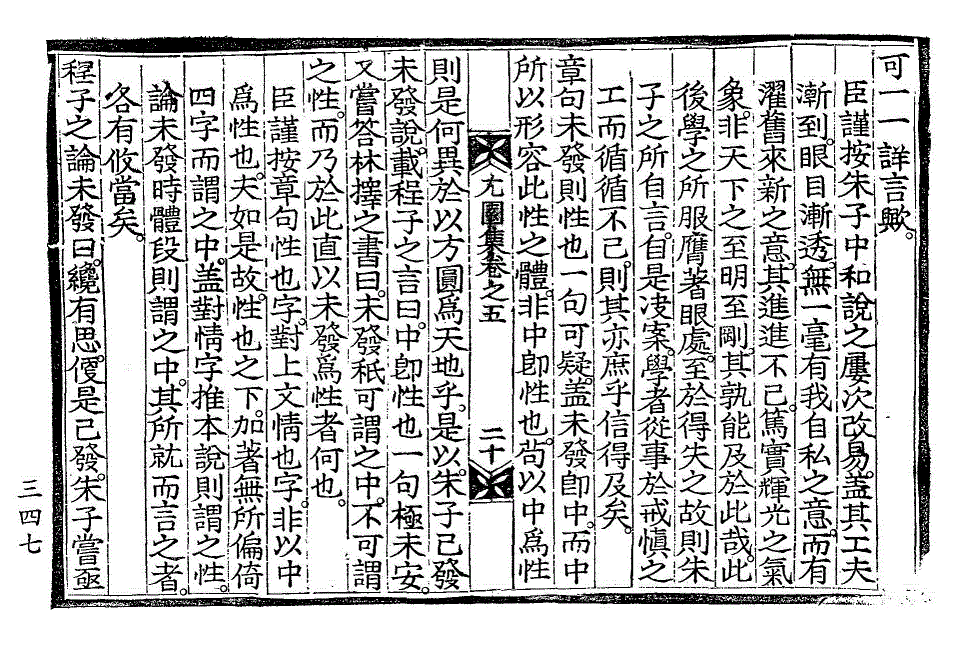 可一一详言欤。
可一一详言欤。臣谨按朱子中和说之屡次改易。盖其工夫渐到。眼目渐透。无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有濯旧来新之意。其进进不已。笃实辉光之气象。非天下之至明至刚。其孰能及于此哉。此后学之所服膺著眼处。至于得失之故则朱子之所自言。自是决案。学者从事于戒慎之工而循循不已。则其亦庶乎信得及矣。
章句未发则性也一句可疑。盖未发即中。而中所以形容此性之体。非中即性也。苟以中为性则是何异于以方圆为天地乎。是以。朱子已发未发说。载程子之言曰。中即性也一句极未安。又尝答林择之书曰。未发秖可谓之中。不可谓之性。而乃于此直以未发为性者何也。
臣谨按章句性也字。对上文情也字。非以中为性也。夫如是故。性也之下。加著无所偏倚四字而谓之中。盖对情字推本说则谓之性。论未发时体段则谓之中。其所就而言之者。各有攸当矣。
程子之论未发曰。才有思。便是已发。朱子尝亟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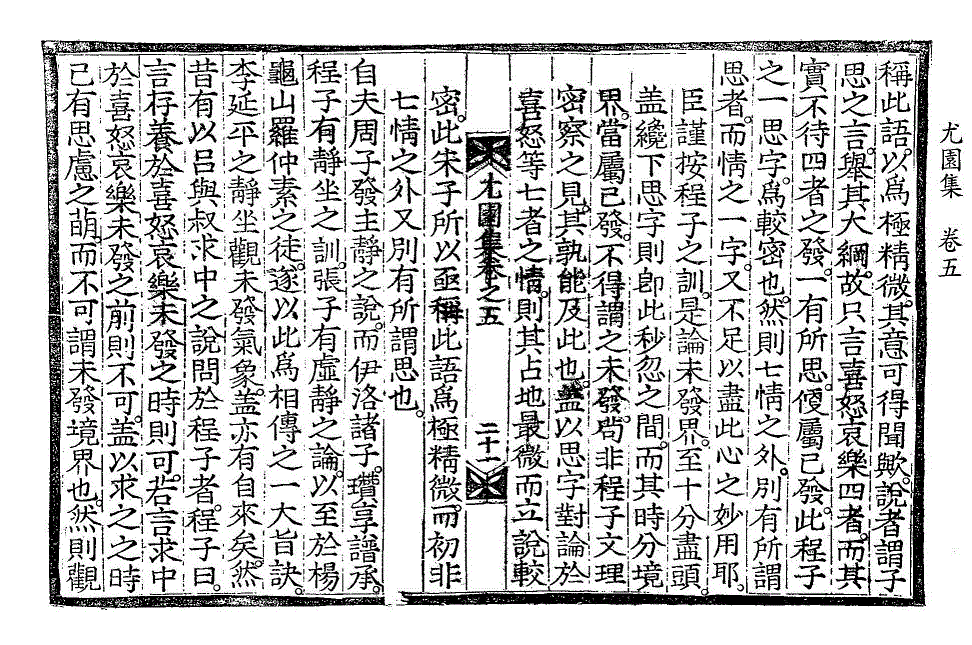 称此语。以为极精微。其意可得闻欤。说者谓子思之言。举其大纲。故只言喜怒哀乐四者。而其实不待四者之发。一有所思。便属已发。此程子之一思字。为较密也。然则七情之外。别有所谓思者。而情之一字。又不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
称此语。以为极精微。其意可得闻欤。说者谓子思之言。举其大纲。故只言喜怒哀乐四者。而其实不待四者之发。一有所思。便属已发。此程子之一思字。为较密也。然则七情之外。别有所谓思者。而情之一字。又不足以尽此心之妙用耶。臣谨按程子之训。是论未发界。至十分尽头。盖才下思字则即此秒忽之间。而其时分境界。当属已发。不得谓之未发。苟非程子文理密察之见。其孰能及此也。盖以思字对论于喜怒等七者之情。则其占地最微而立说较密。此朱子所以亟称此语为极精微。而初非七情之外又别有所谓思也。
自夫周子发主静之说。而伊洛诸子。瓒享谱承。程子有静坐之训。张子有虚静之论。以至于杨龟山罗仲素之徒。遂以此为相传之一大旨诀。李延平之静坐观未发气象。盖亦有自来矣。然昔有以吕与叔求中之说问于程子者。程子曰。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盖以求之之时已有思虑之萌。而不可谓未发境界也。然则观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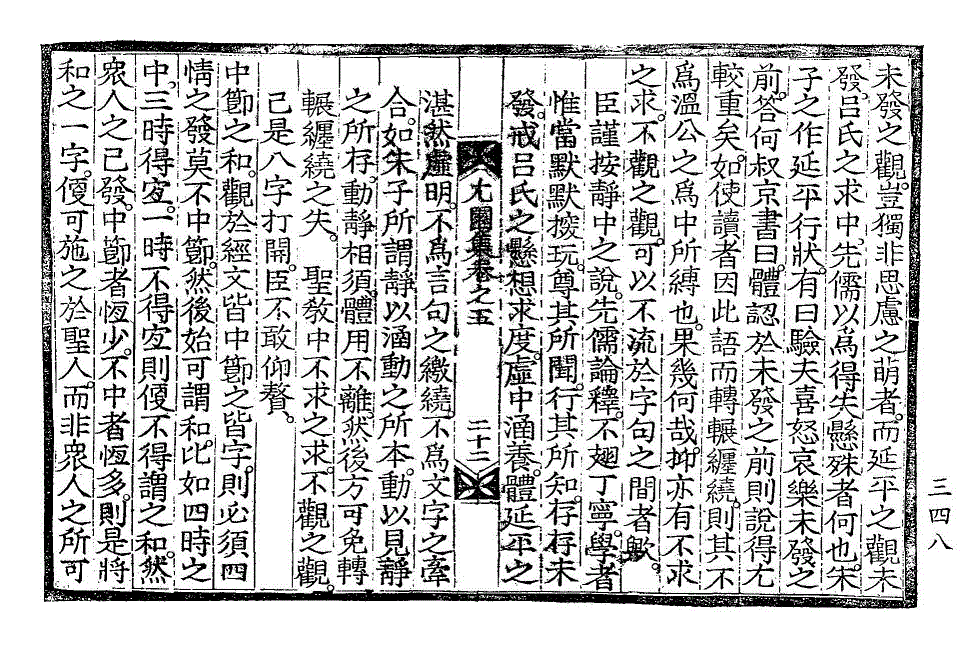 未发之观。岂独非思虑之萌者。而延平之观未发。吕氏之求中。先儒以为得失悬殊者何也。朱子之作延平行状。有曰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答何叔京书曰。体认于未发之前则说得尤较重矣。如使读者因此语而转辗缠绕。则其不为温公之为中所缚也。果几何哉。抑亦有不求之求。不观之观。可以不流于字句之间者欤。
未发之观。岂独非思虑之萌者。而延平之观未发。吕氏之求中。先儒以为得失悬殊者何也。朱子之作延平行状。有曰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答何叔京书曰。体认于未发之前则说得尤较重矣。如使读者因此语而转辗缠绕。则其不为温公之为中所缚也。果几何哉。抑亦有不求之求。不观之观。可以不流于字句之间者欤。臣谨按静中之说。先儒论释。不翅丁宁。学者惟当默默探玩。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存存未发。戒吕氏之悬想求度。虚中涵养。体延平之湛然虚明。不为言句之缴绕。不为文字之牵合。如朱子所谓静以涵动之所本。动以见静之所存。动静相须。体用不离。然后方可免转辗缠绕之失。 圣教中不求之求。不观之观。已是八字打开。臣不敢仰赘。
中节之和。观于经文皆中节之皆字。则必须四情之发莫不中节。然后始可谓和。比如四时之中。三时得宜。一时不得宜则便不得谓之和。然众人之已发。中节者恒少。不中者恒多。则是将和之一字。便可施之于圣人。而非众人之所可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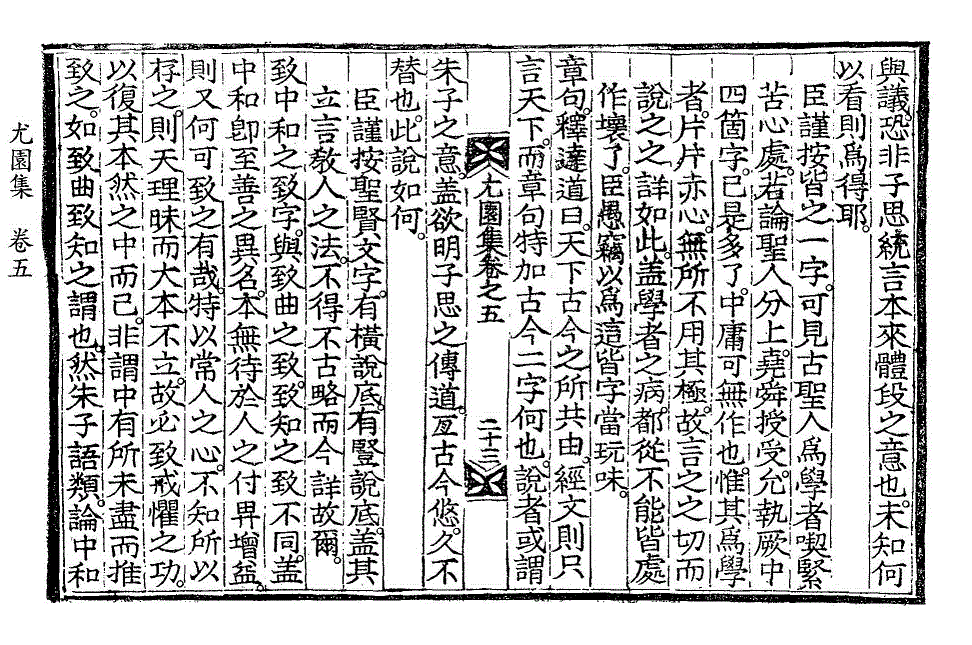 与议。恐非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也。未知何以看则为得耶。
与议。恐非子思统言本来体段之意也。未知何以看则为得耶。臣谨按皆之一字。可见古圣人为学者吃紧苦心处。若论圣人分上。尧舜授受。允执厥中四个字。已是多了。中庸可无作也。惟其为学者。片片赤心。无所不用其极。故言之之切而说之之详如此。盖学者之病。都从不能皆处作坏了。臣愚窃以为这皆字当玩味。
章句。释达道曰。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经文则只言天下。而章句特加古今二字何也。说者或谓朱子之意。盖欲明子思之传道。亘古今悠。久不替也。此说如何。
臣谨按圣贤文字。有横说底。有竖说底。盖其立言教人之法。不得不古略而今详故尔。
致中和之致字。与致曲之致。致知之致不同。盖中和即至善之异名。本无待于人之付畀增益。则又何可致之有哉。特以常人之心。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不立。故必致戒惧之功。以复其本然之中而已。非谓中有所未尽而推致之。如致曲致知之谓也。然朱子语类。论中和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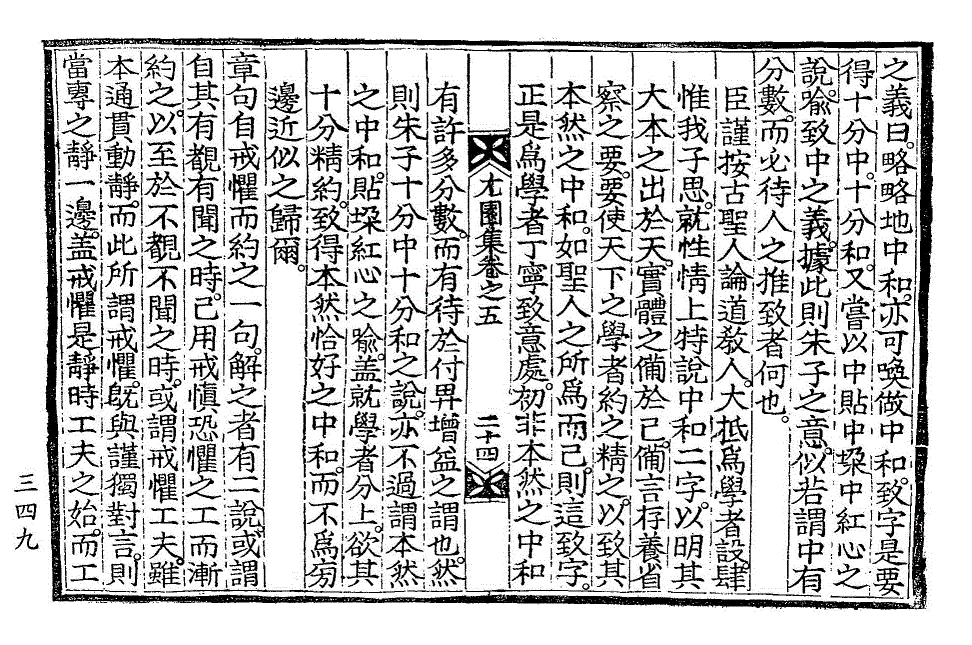 之义曰。略略地中和。亦可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尝以中贴中垛中红心之说。喻致中之义。据此则朱子之意。似若谓中有分数。而必待人之推致者何也。
之义曰。略略地中和。亦可唤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尝以中贴中垛中红心之说。喻致中之义。据此则朱子之意。似若谓中有分数。而必待人之推致者何也。臣谨按古圣人论道教人。大抵为学者设。肆惟我子思。就性情上特说中和二字。以明其大本之出于天。实体之备于己。备言存养省察之要。要使天下之学者约之精之。以致其本然之中和。如圣人之所为而已。则这致字。正是为学者丁宁致意处。初非本然之中和有许多分数。而有待于付畀增益之谓也。然则朱子十分中十分和之说。亦不过谓本然之中和。贴垛红心之喻。盖就学者分上。欲其十分精约。致得本然恰好之中和。而不为旁边近似之归尔。
章句自戒惧而约之一句。解之者有二说。或谓自其有睹有闻之时。已用戒慎恐惧之工而渐约之。以至于不睹不闻之时。或谓戒惧工夫。虽本通贯动静。而此所谓戒惧。既与谨独对言。则当专之静一边。盖戒惧是静时工夫之始。而工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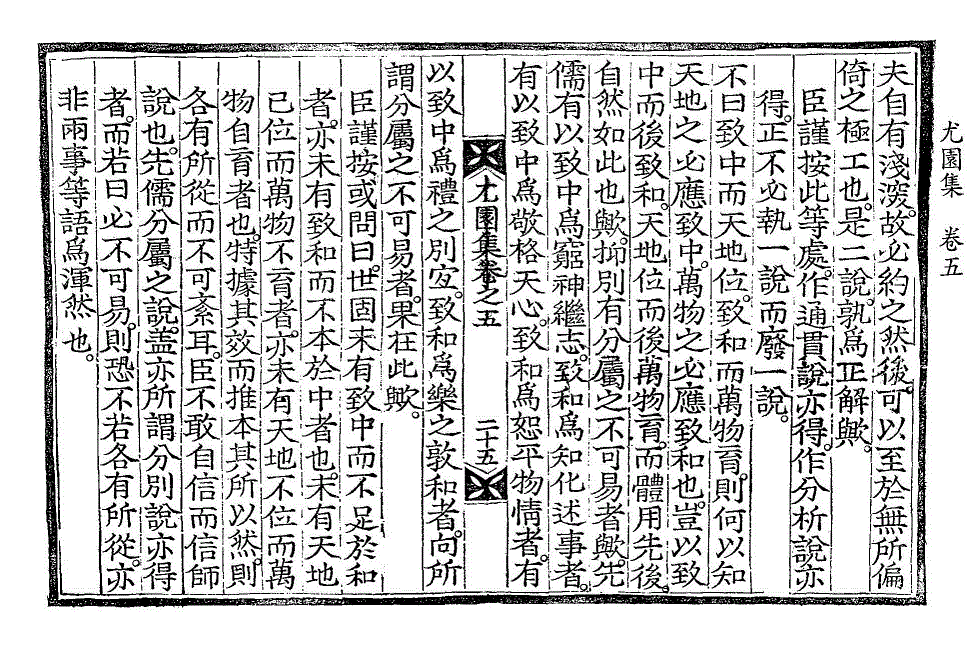 夫自有浅深。故必约之然后。可以至于无所偏倚之极工也。是二说。孰为正解欤。
夫自有浅深。故必约之然后。可以至于无所偏倚之极工也。是二说。孰为正解欤。臣谨按此等处。作通贯说亦得。作分析说亦得。正不必执一说而废一说。
不曰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万物育。则何以知天地之必应致中。万物之必应致和也。岂以致中而后致和。天地位而后万物育。而体用先后。自然如此也欤。抑别有分属之不可易者欤。先儒有以致中为穷神继志。致和为知化述事者。有以致中为敬格天心。致和为恕平物情者。有以致中为礼之别宜。致和为乐之敦和者。向所谓分属之不可易者。果在此欤。
臣谨按或问曰。世固未有致中而不足于和者。亦未有致和而不本于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万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万物自育者也。特据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则各有所从而不可紊耳。臣不敢自信而信师说也。先儒分属之说。盖亦所谓分别说亦得者。而若曰必不可易。则恐不若各有所从。亦非两事等语为浑然也。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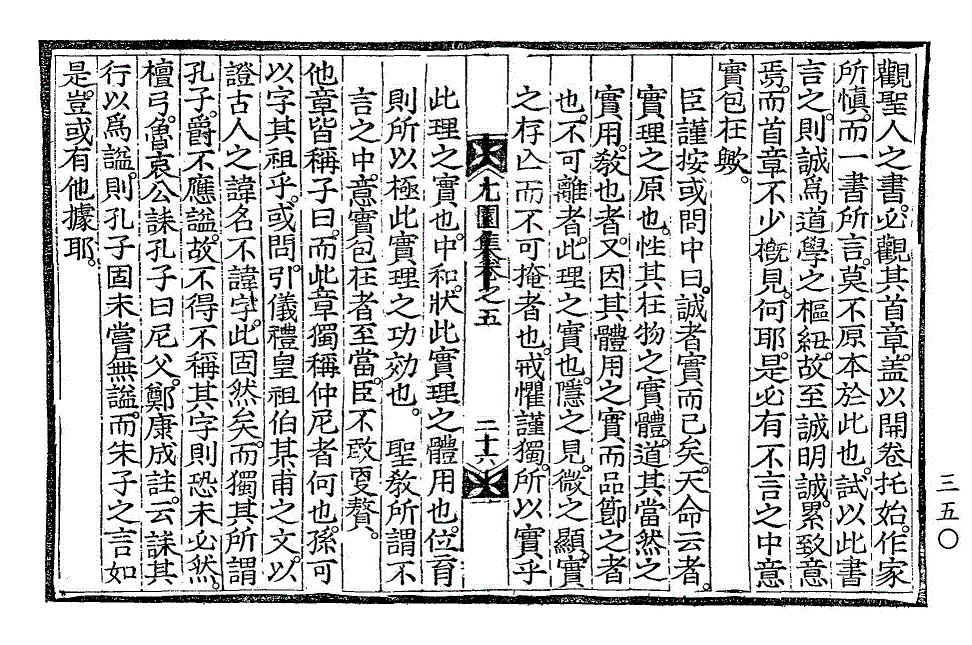 观圣人之书。必观其首章。盖以开卷托始。作家所慎。而一书所言。莫不原本于此也。试以此书言之。则诚为道学之枢纽。故至诚明诚。累致意焉。而首章不少概见。何耶。是必有不言之中意实包在欤。
观圣人之书。必观其首章。盖以开卷托始。作家所慎。而一书所言。莫不原本于此也。试以此书言之。则诚为道学之枢纽。故至诚明诚。累致意焉。而首章不少概见。何耶。是必有不言之中意实包在欤。臣谨按或问中曰。诚者实而已矣。天命云者。实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实体。道其当然之实用。教也者。又因其体用之实而品节之者也。不可离者。此理之实也。隐之见。微之显。实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惧谨独。所以实乎此理之实也。中和。状此实理之体用也。位育则所以极此实理之功效也。 圣教所谓不言之中。意实包在者至当。臣不敢更赘。
他章皆称子曰。而此章独称仲尼者何也。孙可以字其祖乎。或问。引仪礼皇祖伯某甫之文。以證古人之讳名不讳字。此固然矣。而独其所谓孔子。爵不应谥。故不得不称其字则恐未必然。檀弓。鲁哀公诔孔子曰尼父。郑康成注。云诔其行以为谥。则孔子固未尝无谥。而朱子之言如是。岂或有他据耶。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1H 页
 臣谨按朱子之不取郑说。臣不敢臆断。然父之为谥。未见其分明。如诗之皇父尚父。史之仲父。仪礼之某父。皆尊敬之称。而未见其为谥也。故尚父,仲父。皆别有谥焉。况孔子爵不应谥则其不以父为谥也明矣。夫岂无稽而朱子取之哉。
臣谨按朱子之不取郑说。臣不敢臆断。然父之为谥。未见其分明。如诗之皇父尚父。史之仲父。仪礼之某父。皆尊敬之称。而未见其为谥也。故尚父,仲父。皆别有谥焉。况孔子爵不应谥则其不以父为谥也明矣。夫岂无稽而朱子取之哉。首章专言理。此章兼言气质。盖君子小人之分。专由于气质之不同。而此章既以君子小人对言。则不可谓专言本然之理也明矣。或云此章之君子小人。秖言敬肆之分。而未及乎气质。至第四章知愚贤不肖之过不及。然后始言气质。故章句所谓生禀之异者。在第四章而不在此章。此其说似矣。而但君子之所以敬。小人之所以肆。究其所由。不外乎气质之不同。则穷本探原之论。不得不以此章为兼言气质。未知如何。
臣谨按君子之所以敬。小人之所以肆。不外乎气质之不同。 圣教至当。但此章立言之本旨。重在于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敬肆毫釐之间。盖曰。中庸是天命人心自在之正理。而惟君子之克念克敬者。为能体之。小人之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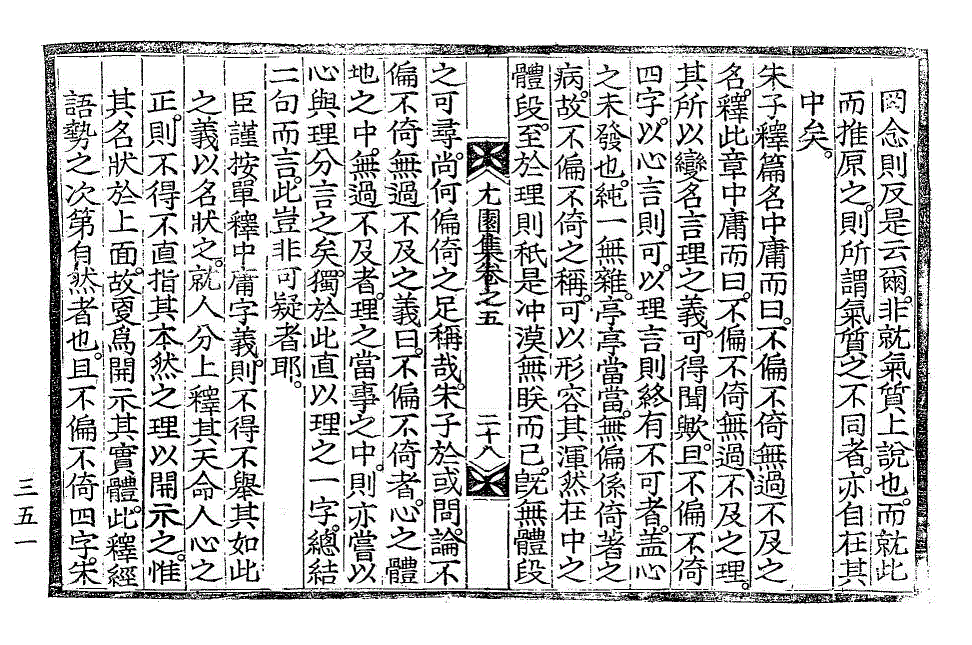 罔念则反是云尔。非就气质上说也。而就此而推原之。则所谓气质之不同者。亦自在其中矣。
罔念则反是云尔。非就气质上说也。而就此而推原之。则所谓气质之不同者。亦自在其中矣。朱子释篇名中庸而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释此章中庸而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理。其所以变名言理之义。可得闻欤。且不偏不倚四字。以心言则可。以理言则终有不可者。盖心之未发也。纯一无杂。亭亭当当。无偏系倚著之病。故不偏不倚之称。可以形容其浑然在中之体段。至于理则秖是冲漠无眹而已。既无体段之可寻。尚何偏倚之足称哉。朱子于或问。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曰。不偏不倚者。心之体地之中。无过不及者。理之当事之中。则亦尝以心与理分言之矣。独于此直以理之一字。总结二句而言。此岂非可疑者耶。
臣谨按单释中庸字义。则不得不举其如此之义以名状之。就人分上释其天命人心之正。则不得不直指其本然之理以开示之。惟其名状于上面。故更为开示其实体。此释经语势之次第自然者也。且不偏不倚四字。朱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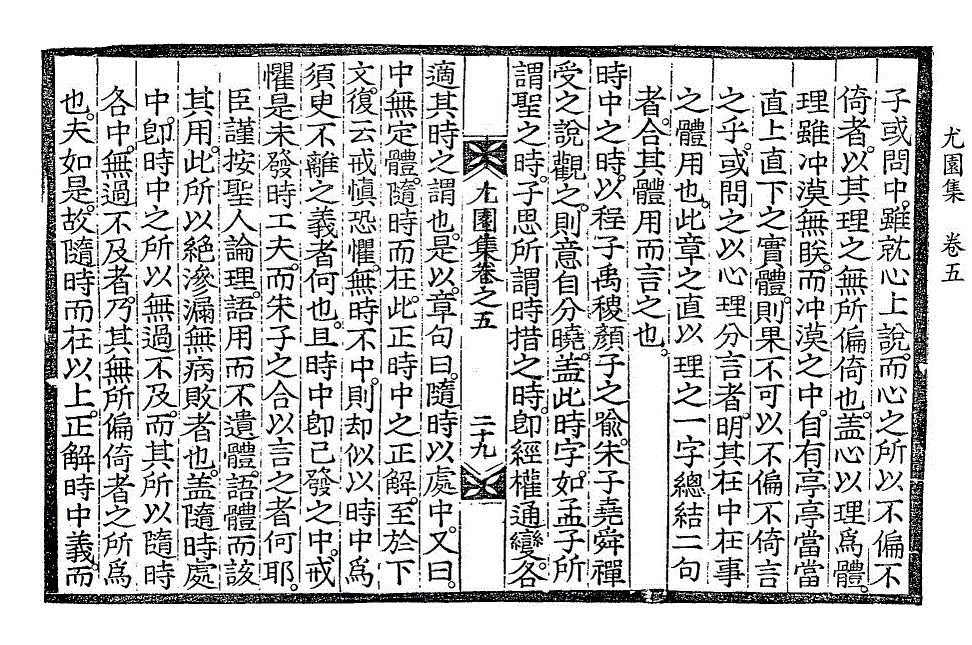 子或问中。虽就心上说。而心之所以不偏不倚者。以其理之无所偏倚也。盖心以理为体。理虽冲漠无眹。而冲漠之中。自有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实体。则果不可以不偏不倚言之乎。或问之以心理分言者。明其在中在事之体用也。此章之直以理之一字总结二句者。合其体用而言之也。
子或问中。虽就心上说。而心之所以不偏不倚者。以其理之无所偏倚也。盖心以理为体。理虽冲漠无眹。而冲漠之中。自有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实体。则果不可以不偏不倚言之乎。或问之以心理分言者。明其在中在事之体用也。此章之直以理之一字总结二句者。合其体用而言之也。时中之时。以程子禹稷颜子之喻。朱子尧舜禅受之说观之。则意自分晓。盖此时字。如孟子所谓圣之时。子思所谓时措之时。即经权通变。各适其时之谓也。是以。章句曰。随时以处中。又曰。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此正时中之正解。至于下文。复云戒慎恐惧。无时不中。则却似以时中为须臾不离之义者何也。且时中即已发之中。戒惧是未发时工夫。而朱子之合以言之者何耶。
臣谨按圣人论理。语用而不遗体。语体而该其用。此所以绝渗漏无病败者也。盖随时处中。即时中之所以无过不及。而其所以随时各中。无过不及者。乃其无所偏倚者之所为也。夫如是。故随时而在以上。正解时中义。而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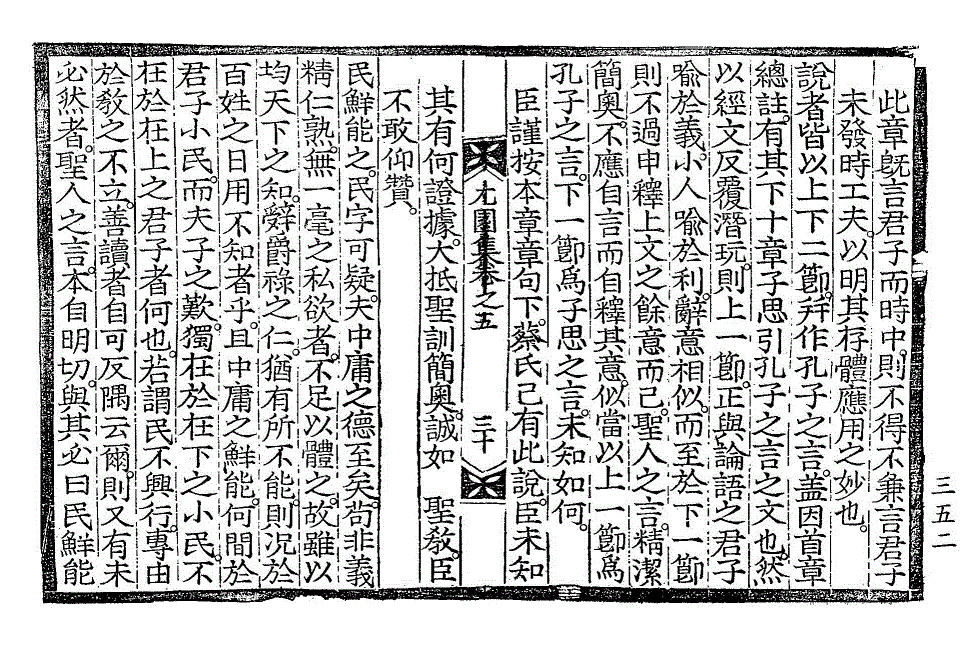 此章既言君子而时中。则不得不兼言君子未发时工夫。以明其存体应用之妙也。
此章既言君子而时中。则不得不兼言君子未发时工夫。以明其存体应用之妙也。说者皆以上下二节。并作孔子之言。盖因首章总注。有其下十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之文也。然以经文反覆潜玩。则上一节。正与论语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辞意相似。而至于下一节则不过申释上文之馀意而已。圣人之言。精洁简奥。不应自言而自释其意。似当以上一节为孔子之言。下一节为子思之言。未知如何。
臣谨按本章章句下。蔡氏已有此说。臣未知其有何證据。大抵圣训简奥。诚如 圣教。臣不敢仰赞。
民鲜能之。民字可疑。夫中庸之德至矣。苟非义精仁熟。无一毫之私欲者。不足以体之。故虽以均天下之知。辞爵禄之仁。犹有所不能。则况于百姓之日用不知者乎。且中庸之鲜能。何间于君子小民。而夫子之叹。独在于在下之小民。不在于在上之君子者何也。若谓民不兴行。专由于教之不立。善读者自可反隅云尔。则又有未必然者。圣人之言。本自明切。与其必曰民鲜能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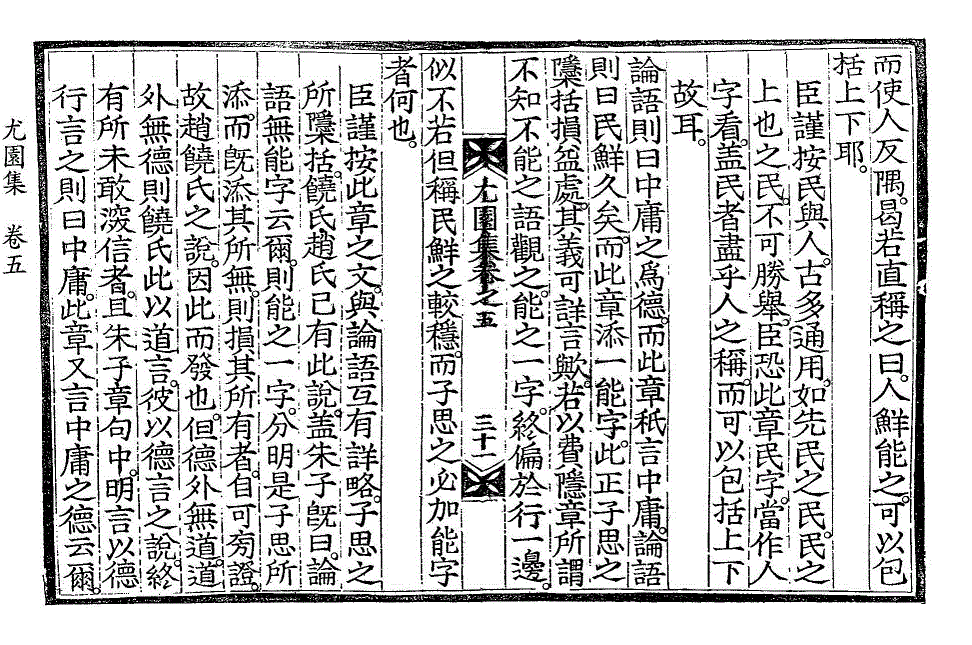 而使人反隅。曷若直称之曰。人鲜能之。可以包括上下耶。
而使人反隅。曷若直称之曰。人鲜能之。可以包括上下耶。臣谨按民与人。古多通用。如先民之民。民之上也之民。不可胜举。臣恐此章民字。当作人字看。盖民者尽乎人之称。而可以包括上下故耳。
论语则曰中庸之为德。而此章秖言中庸。论语则曰民鲜久矣。而此章添一能字。此正子思之檃括损益处。其义可详言欤。若以费隐章所谓不知不能之语观之。能之一字。终偏于行一边。似不若但称民鲜之较稳。而子思之必加能字者何也。
臣谨按此章之文。与论语互有详略。子思之所檃括。饶氏,赵氏已有此说。盖朱子既曰。论语无能字云尔。则能之一字。分明是子思所添。而既添其所无。则损其所有者。自可旁證。故赵饶氏之说。因此而发也。但德外无道。道外无德则饶氏此以道言。彼以德言之说。终有所未敢深信者。且朱子章句中。明言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此章又言中庸之德云尔。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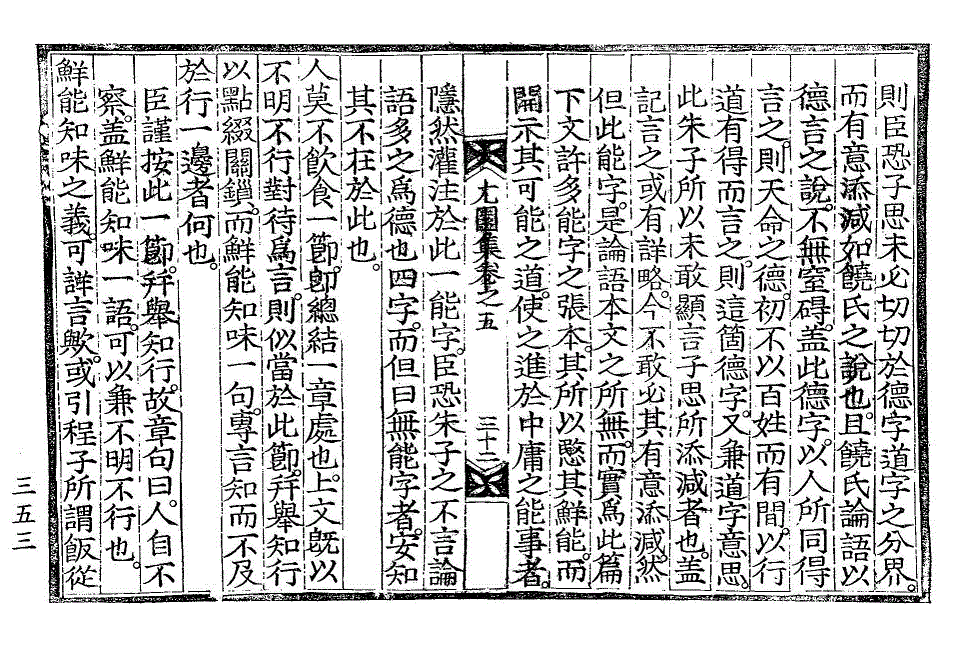 则臣恐子思未必切切于德字道字之分界。而有意添减。如饶氏之说也。且饶氏论语以德言之说。不无窒碍。盖此德字。以人所同得言之。则天命之德。初不以百姓而有间。以行道有得而言之。则这个德字。又兼道字意思。此朱子所以未敢显言子思所添减者也。盖记言之或有详略。今不敢必其有意添减。然但此能字。是论语本文之所无。而实为此篇下文许多能字之张本。其所以悯其鲜能。而开示其可能之道。使之进于中庸之能事者。隐然灌注于此一能字。臣恐朱子之不言论语多之为德也四字。而但曰无能字者。安知其不在于此也。
则臣恐子思未必切切于德字道字之分界。而有意添减。如饶氏之说也。且饶氏论语以德言之说。不无窒碍。盖此德字。以人所同得言之。则天命之德。初不以百姓而有间。以行道有得而言之。则这个德字。又兼道字意思。此朱子所以未敢显言子思所添减者也。盖记言之或有详略。今不敢必其有意添减。然但此能字。是论语本文之所无。而实为此篇下文许多能字之张本。其所以悯其鲜能。而开示其可能之道。使之进于中庸之能事者。隐然灌注于此一能字。臣恐朱子之不言论语多之为德也四字。而但曰无能字者。安知其不在于此也。人莫不饮食一节。即总结一章处也。上文既以不明不行对待为言。则似当于此节。并举知行以点缀关锁。而鲜能知味一句。专言知而不及于行一边者何也。
臣谨按此一节。并举知行。故章句曰。人自不察。盖鲜能知味一语。可以兼不明不行也。
鲜能知味之义。可详言欤。或引程子所谓饭从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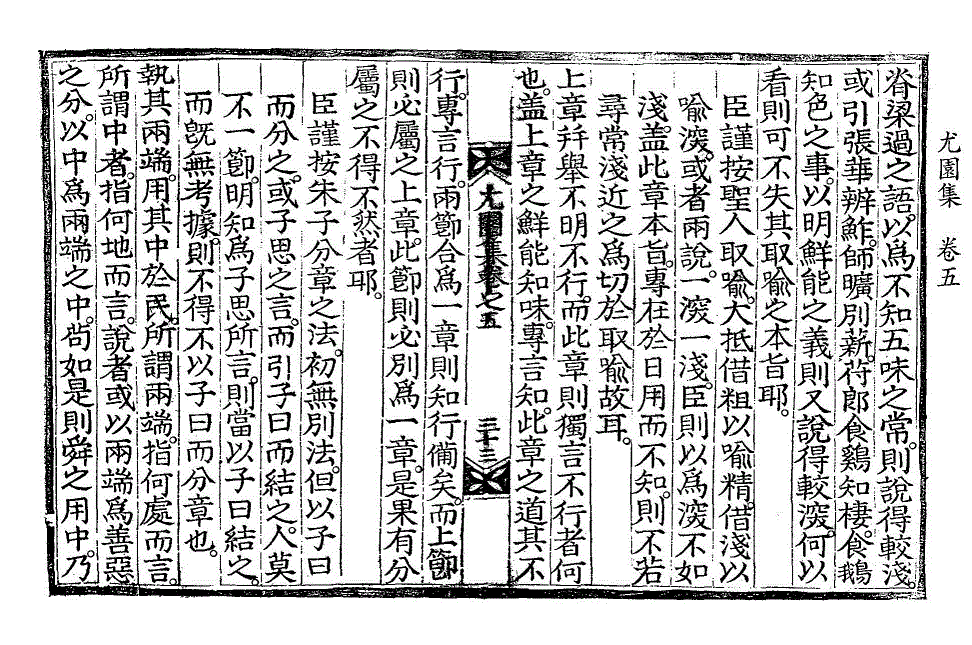 脊梁过之语。以为不知五味之常。则说得较浅。或引张华辨鲊。师旷别薪。苻郎食鸡知栖。食鹅知色之事。以明鲜能之义则又说得较深。何以看则可不失其取喻之本旨耶。
脊梁过之语。以为不知五味之常。则说得较浅。或引张华辨鲊。师旷别薪。苻郎食鸡知栖。食鹅知色之事。以明鲜能之义则又说得较深。何以看则可不失其取喻之本旨耶。臣谨按圣人取喻。大抵借粗以喻精。借浅以喻深。或者两说。一深一浅。臣则以为深不如浅。盖此章本旨。专在于日用而不知。则不若寻常浅近之为切于取喻故耳。
上章并举不明不行。而此章则独言不行者何也。盖上章之鲜能知味。专言知。此章之道其不行。专言行。两节合为一章则知行备矣。而上节则必属之上章。此节则必别为一章。是果有分属之不得不然者耶。
臣谨按朱子公章之法。初无别法。但以子曰而分之。或子思之言。而引子曰而结之。人莫不一节。明知为子思所言。则当以子曰结之。而既无考据。则不得不以子曰而分章也。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谓两端。指何处而言。所谓中者。指何地而言。说者或以两端为善恶之分。以中为两端之中。苟如是则舜之用中。乃
尤园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3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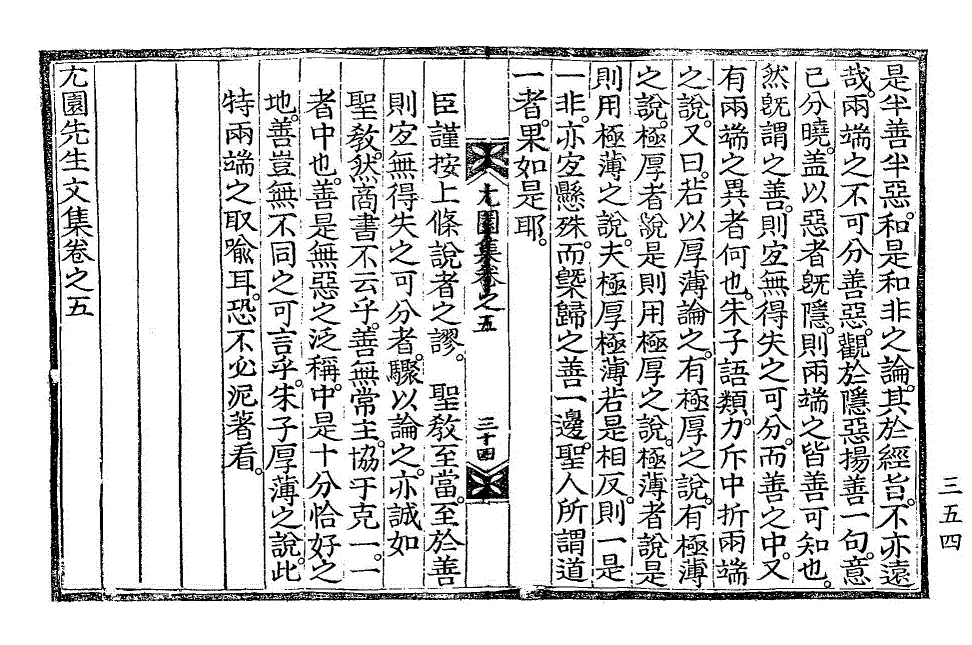 是半善半恶。和是和非之论。其于经旨。不亦远哉。两端之不可分善恶。观于隐恶扬善一句。意已分晓。盖以恶者既隐。则两端之皆善可知也。然既谓之善。则宜无得失之可分。而善之中。又有两端之异者何也。朱子语类。力斥中折两端之说。又曰。若以厚薄论之。有极厚之说。有极薄之说。极厚者说是则用极厚之说。极薄者说是则用极薄之说。夫极厚极薄若是相反。则一是一非。亦宜悬殊。而槩归之善一边。圣人所谓道一者。果如是耶。
是半善半恶。和是和非之论。其于经旨。不亦远哉。两端之不可分善恶。观于隐恶扬善一句。意已分晓。盖以恶者既隐。则两端之皆善可知也。然既谓之善。则宜无得失之可分。而善之中。又有两端之异者何也。朱子语类。力斥中折两端之说。又曰。若以厚薄论之。有极厚之说。有极薄之说。极厚者说是则用极厚之说。极薄者说是则用极薄之说。夫极厚极薄若是相反。则一是一非。亦宜悬殊。而槩归之善一边。圣人所谓道一者。果如是耶。臣谨按上条说者之谬。 圣教至当。至于善则宜无得失之可公者。骤以论之。亦诚如 圣教。然商书不云乎。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一者中也。善是无恶之泛称。中是十分恰好之地。善岂无不同之可言乎。朱子厚薄之说。此特两端之取喻耳。恐不必泥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