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典庵文集卷之七
杂著
杂著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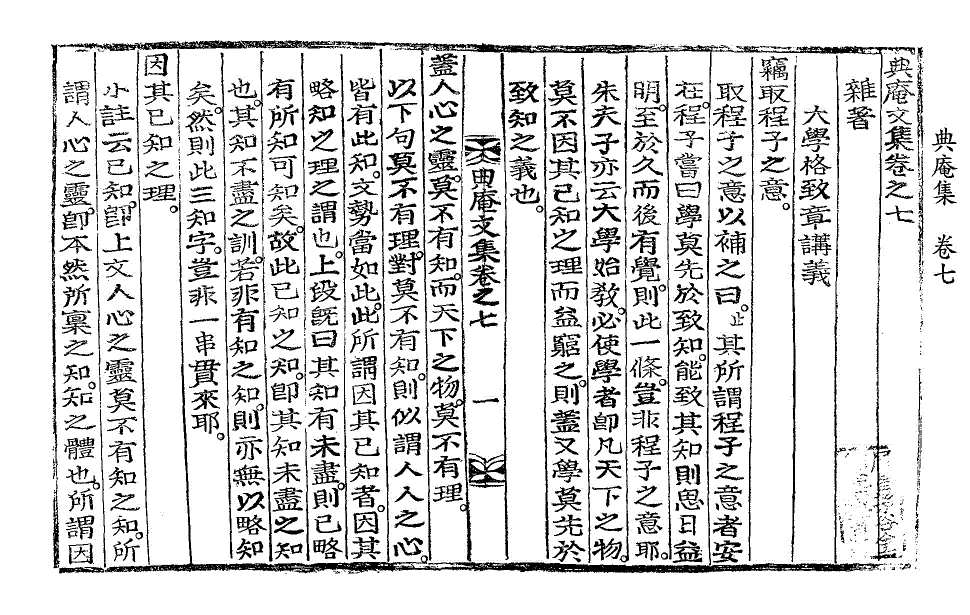 大学格致章讲义
大学格致章讲义窃取程子之意。
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止。)其所谓程子之意者安在。程子尝曰学莫先于致知。能致其知则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后有觉。则此一条。岂非程子之意耶。朱夫子亦云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则盖又学莫先于致知之义也。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以下句莫不有理。对莫不有知。则似谓人人之心。皆有此知。文势当如此。此所谓因其已知者。因其略知之理之谓也。上段既曰其知有未尽。则已略有所知可知矣。故此已知之知。即其知未尽之知也。其知不尽之训。若非有知之知。则亦无以略知矣。然则此三知字。岂非一串贯来耶。
因其已知之理。
小注云已知。即上文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之知。所谓人心之灵。即本然所禀之知。知之体也。所谓因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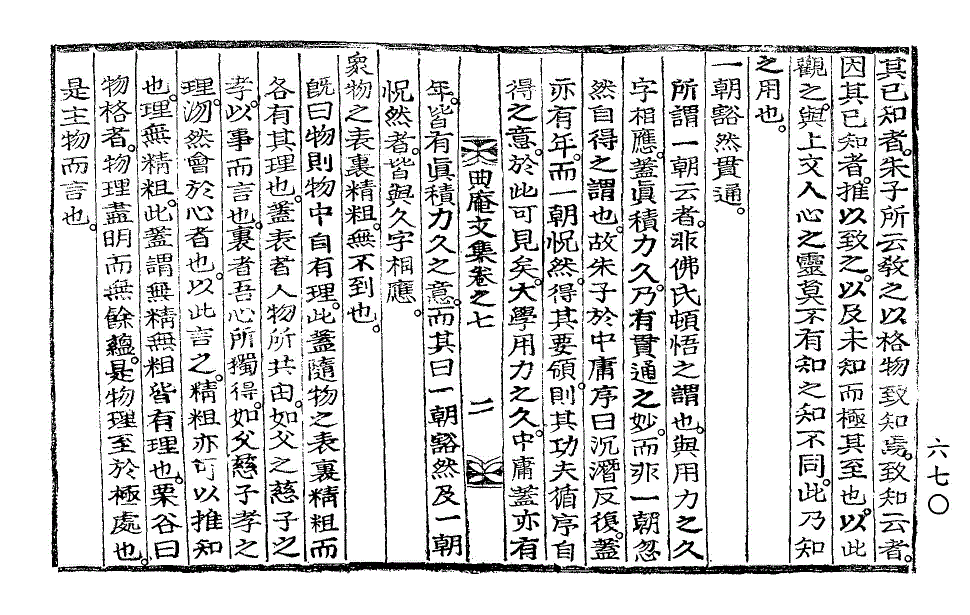 其已知者。朱子所云教之以格物致知焉。致知云者。因其已知者。推以致之。以及未知而极其至也。以此观之。与上文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之知不同。此乃知之用也。
其已知者。朱子所云教之以格物致知焉。致知云者。因其已知者。推以致之。以及未知而极其至也。以此观之。与上文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之知不同。此乃知之用也。一朝豁然贯通。
所谓一朝云者。非佛氏顿悟之谓也。与用力之久字相应。盖真积力久。乃有贯通之妙。而非一朝忽然自得之谓也。故朱子于中庸序曰沉潜反复。盖亦有年。而一朝恍然。得其要领。则其功夫循序自得之意。于此可见矣。大学用力之久。中庸盖亦有年。皆有真积力久之意。而其曰一朝豁然及一朝恍然者。皆与久字相应。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
既曰物则物中自有理。此盖随物之表里精粗而各有其理也。盖表者人物所共由。如父之慈子之孝。以事而言也。里者吾心所独得。如父慈子孝之理。沕然会于心者也。以此言之。精粗亦可以推知也。理无精粗。此盖谓无精无粗皆有理也。栗谷曰物格者。物理尽明而无馀蕴。是物理至于极处也。是主物而言也。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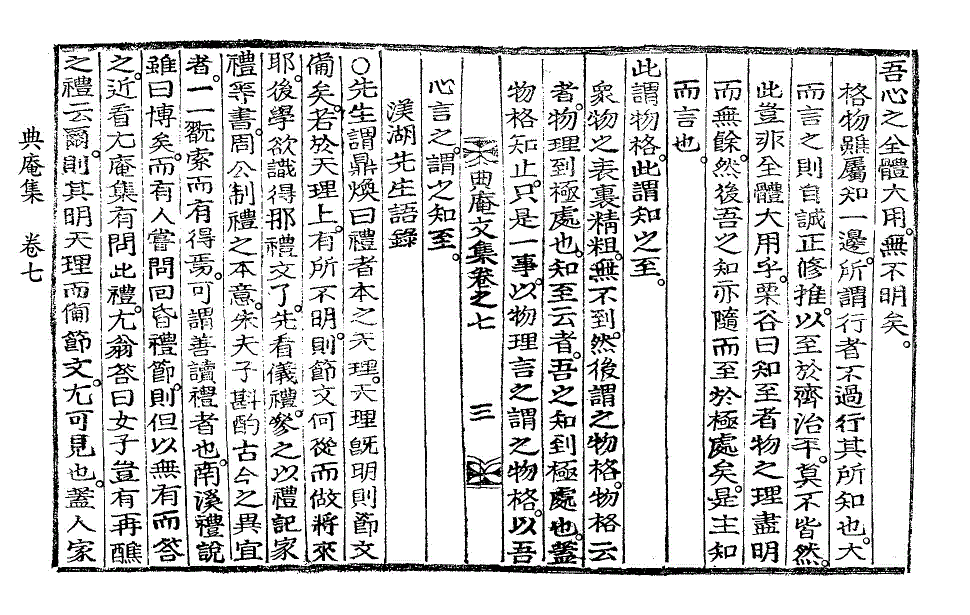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格物虽属知一边。所谓行者不过行其所知也。大而言之则自诚正修推。以至于齐治平。莫不皆然。此岂非全体大用乎。栗谷曰知至者物之理尽明而无馀。然后吾之知亦随而至于极处矣。是主知而言也。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然后谓之物格。物格云者。物理到极处也。知至云者。吾之知到极处也。盖物格知止。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谓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谓之知至。
渼湖先生语录
○先生谓鼎焕曰礼者本之天理。天理既明则节文备矣。若于天理上。有所不明。则节文何从而做将来耶。后学欲识得那礼文了。先看仪礼。参之以礼记家礼等书。周公制礼之本意。朱夫子斟酌古今之异宜者。一一玩索而有得焉。可谓善读礼者也。南溪礼说虽曰博矣。而有人尝问回昏礼节。则但以无有而答之。近看尤庵集有问此礼。尤翁答曰女子岂有再醮之礼云尔。则其明天理而备节文。尤可见也。盖人家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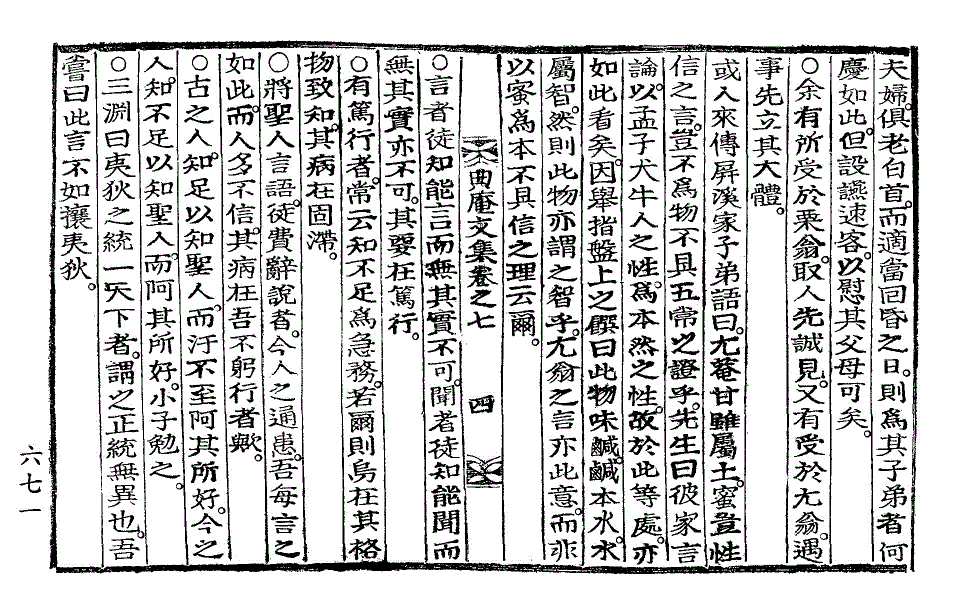 夫妇。俱老白首。而适当回昏之日。则为其子弟者何庆如此。但设宴速客。以慰其父母可矣。
夫妇。俱老白首。而适当回昏之日。则为其子弟者何庆如此。但设宴速客。以慰其父母可矣。○余有所受于栗翁。取人先诚见。又有受于尤翁。遇事先立其大体。
或人来传屏溪家子弟语曰。尤庵甘虽属土。蜜岂性信之言。岂不为物不具五常之證乎。先生曰彼家言论。以孟子犬牛人之性。为本然之性。故于此等处。亦如此看矣。因举指盘上之馔曰此物味咸。咸本水。水属智。然则此物亦谓之智乎。尤翁之言亦此意。而非以蜜为本不具信之理云尔。
○言者徒知能言而无其实不可。闻者徒知能闻而无其实亦不可。其要在笃行。
○有笃行者。常云知不足为急务。若尔则乌在其格物致知。其病在固滞。
○将圣人言语。徒费辞说者。今人之通患。吾每言之如此。而人多不信。其病在吾不躬行者欤。
○古之人。知足以知圣人。而污不至阿其所好。今之人。知不足以知圣人。而阿其所好。小子勉之。
○三渊曰夷狄之统一天下者。谓之正统无异也。吾尝曰此言不如攘夷狄。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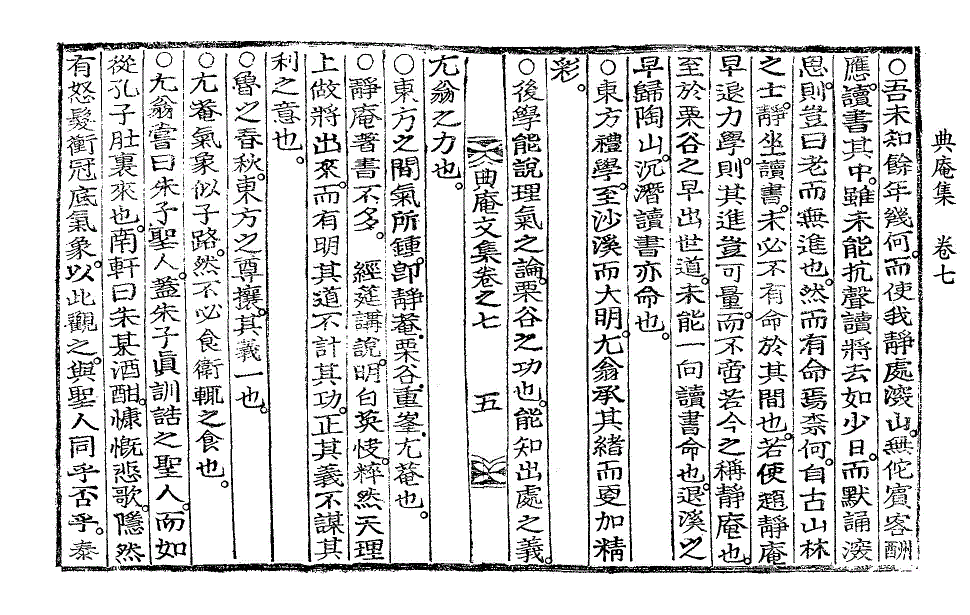 ○吾未知馀年几何。而使我静处深山。无佗宾客酬应。读书其中。虽未能抗声读将去如少日。而默诵深思。则岂曰老而无进也。然而有命焉柰何。自古山林之士。静坐读书。未必不有命于其间也。若使赵静庵早退力学。则其进岂可量。而不啻若今之称静庵也。至于栗谷之早出世道。未能一向读书命也。退溪之早归陶山。沉潜读书亦命也。
○吾未知馀年几何。而使我静处深山。无佗宾客酬应。读书其中。虽未能抗声读将去如少日。而默诵深思。则岂曰老而无进也。然而有命焉柰何。自古山林之士。静坐读书。未必不有命于其间也。若使赵静庵早退力学。则其进岂可量。而不啻若今之称静庵也。至于栗谷之早出世道。未能一向读书命也。退溪之早归陶山。沉潜读书亦命也。○东方礼学。至沙溪而大明。尤翁承其绪而更加精彩。
○后学能说理气之论。栗谷之功也。能知出处之义。尤翁之力也。
○东方之间气所钟。即静庵,栗谷,重峰,尤庵也。
○静庵著书不多。 经筵讲说。明白英快。粹然天理上做将出来。而有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谋其利之意也。
○鲁之春秋。东方之尊攘。其义一也。
○尤庵气象似子路。然不必食卫辄之食也。
○尤翁尝曰朱子圣人。盖朱子真训诰之圣人。而如从孔子肚里来也。南轩曰朱某酒酣。慷慨悲歌。隐然有怒发冲冠底气象。以此观之。与圣人同乎否乎。泰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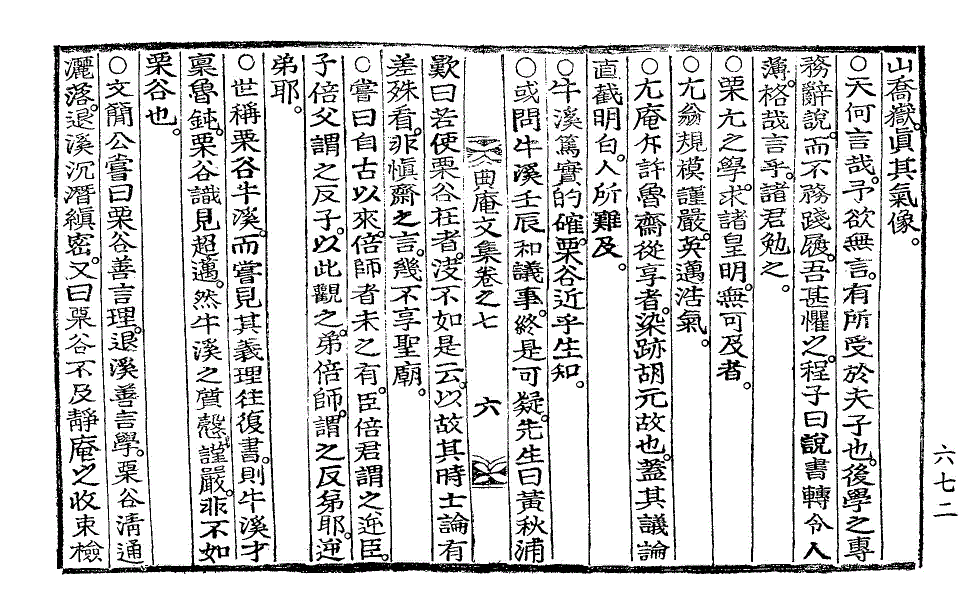 山乔岳。真其气像。
山乔岳。真其气像。○天何言哉。予欲无言。有所受于夫子也。后学之专务辞说。而不务践履。吾甚惧之。程子曰说书转令人薄。格哉言乎。诸君勉之。
○栗尤之学。求诸皇明。无可及者。
○尤翁规模谨严。英迈浩气。
○尤庵斥许鲁斋从享者。染迹胡元故也。盖其议论直截明白。人所难及。
○牛溪笃实的确。栗谷近乎生知。
○或问牛溪壬辰和议事。终是可疑。先生曰黄秋浦叹曰若使栗谷在者。决不如是云。以故其时士论有差殊看。非慎斋之言。几不享圣庙。
○尝曰自古以来。倍师者未之有。臣倍君谓之逆臣。子倍父谓之反子。以此观之。弟倍师。谓之反弟耶。逆弟耶。
○世称栗谷牛溪。而尝见其义理往复书。则牛溪才禀鲁钝。栗谷识见超迈。然牛溪之质悫谨严。非不如栗谷也。
○文𥳑公尝曰栗谷善言理。退溪善言学。栗谷清通洒落。退溪沉潜缜密。又曰栗谷不及静庵之收束检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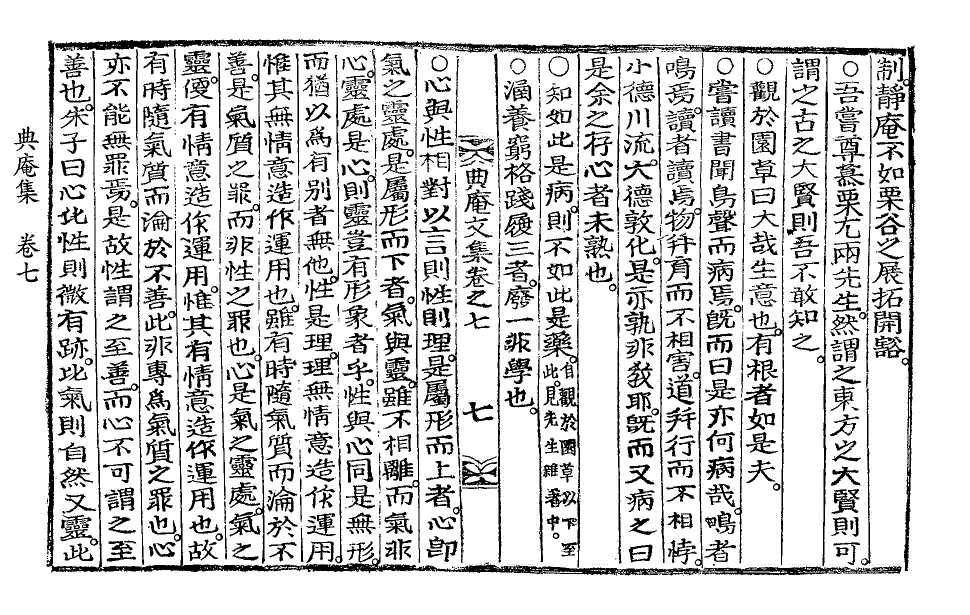 制。静庵不如栗谷之展拓开豁。
制。静庵不如栗谷之展拓开豁。○吾尝尊慕栗尤两先生。然谓之东方之大贤则可。谓之古之大贤则吾不敢知之。
○观于园草曰大哉生意也。有根者如是夫。
○尝读书闻鸟声而病焉。既而曰是亦何病哉。鸣者鸣焉。读者读焉。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亦孰非教耶。既而又病之曰是余之存心者未熟也。
○知如此是病。则不如此是药。(自观于园草以下至此。见先生杂著中。)
○涵养穷格践履三者。废一非学也。
○心与性相对以言则性则理。是属形而上者。心即气之灵处。是属形而下者。气与灵。虽不相离。而气非心。灵处是心。则灵岂有形象者乎。性与心同是无形。而犹以为有别者无他。性是理。理无情意造作运用。惟其无情意造作运用也。虽有时随气质而沦于不善。是气质之罪。而非性之罪也。心是气之灵处。气之灵。便有情意造作运用。惟其有情意造作运用也。故有时随气质而沦于不善。此非专为气质之罪也。心亦不能无罪焉。是故性谓之至善。而心不可谓之至善也。朱子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此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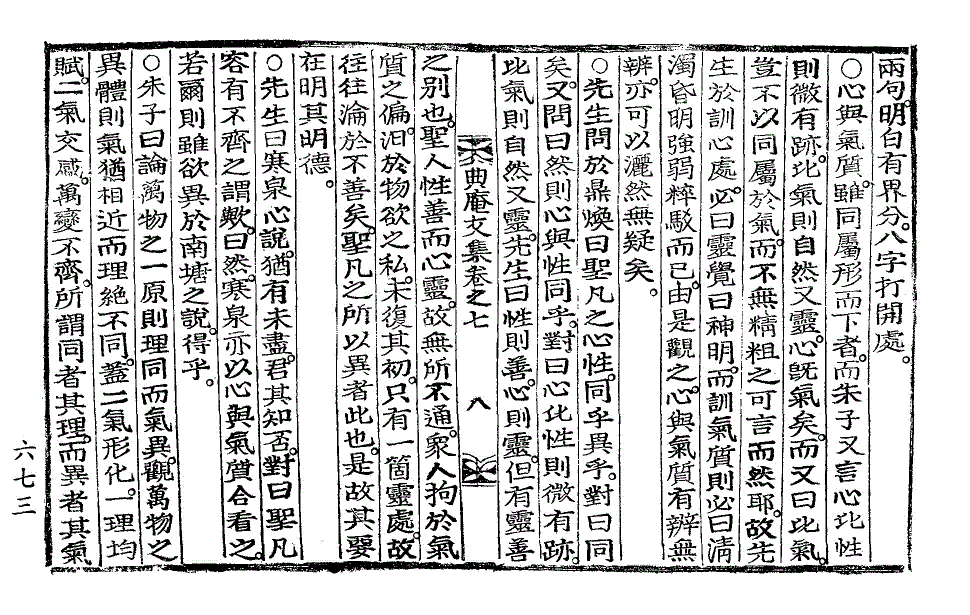 两句。明白有界分。八字打开处。
两句。明白有界分。八字打开处。○心与气质。虽同属形而下者。而朱子又言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心既气矣。而又曰比气。岂不以同属于气。而不无精粗之可言而然耶。故先生于训心处。必曰灵觉曰神明。而训气质则必曰清浊昏明强弱粹驳而已。由是观之。心与气质有辨无辨。亦可以洒然无疑矣。
○先生问于鼎焕曰圣凡之心性。同乎异乎。对曰同矣。又问曰然则心与性同乎。对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先生曰性则善。心则灵。但有灵善之别也。圣人性善而心灵。故无所不通。众人拘于气质之偏。汩于物欲之私。未复其初。只有一个灵处。故往往沦于不善矣。圣凡之所以异者此也。是故其要在明其明德。
○先生曰寒泉心说。犹有未尽。君其知否。对曰圣凡容有不齐之谓欤。曰然。寒泉亦以心与气质合看之。若尔则虽欲异于南塘之说。得乎。
○朱子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盖二气形化。一理均赋。二气交感。万变不齐。所谓同者其理。而异者其气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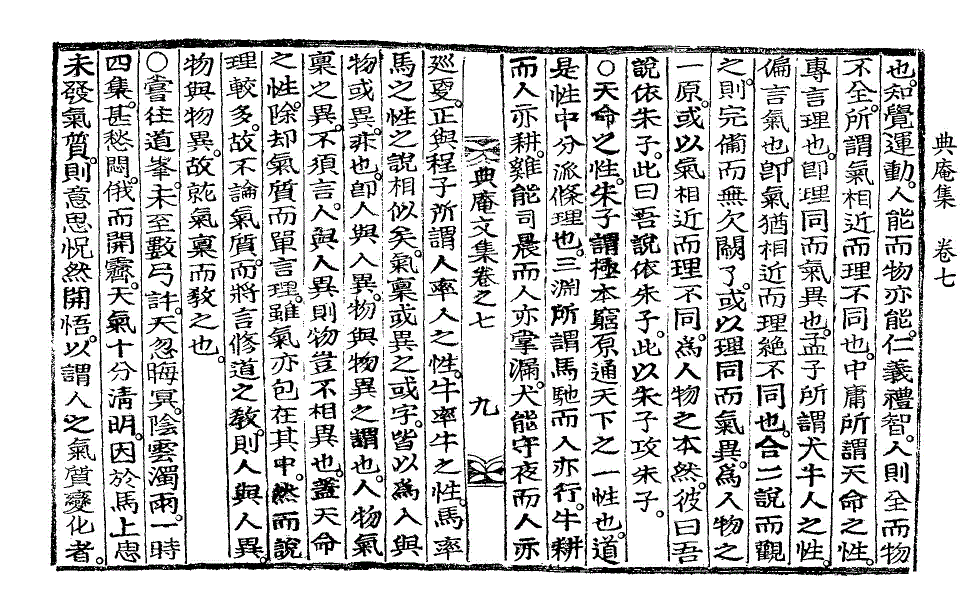 也。知觉运动。人能而物亦能。仁义礼智。人则全而物不全。所谓气相近而理不同也。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专言理也。即理同而气异也。孟子所谓犬牛人之性。偏言气也。即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合二说而观之。则完备而无欠阙了。或以理同而气异。为人物之一原。或以气相近而理不同。为人物之本然。彼曰吾说依朱子。此曰吾说依朱子。此以朱子攻朱子。
也。知觉运动。人能而物亦能。仁义礼智。人则全而物不全。所谓气相近而理不同也。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专言理也。即理同而气异也。孟子所谓犬牛人之性。偏言气也。即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合二说而观之。则完备而无欠阙了。或以理同而气异。为人物之一原。或以气相近而理不同。为人物之本然。彼曰吾说依朱子。此曰吾说依朱子。此以朱子攻朱子。○天命之性。朱子谓极本穷原通天下之一性也。道是性中分派条理也。三渊所谓马驰而人亦行。牛耕而人亦耕。鸡能司晨而人亦掌漏。犬能守夜而人亦巡更。正与程子所谓人率人之性。牛率牛之性。马率马之性之说相似矣。气禀或异之或字。皆以为人与物或异。非也。即人与人异。物与物异之谓也。人物气禀之异。不须言。人与人异则物岂不相异也。盖天命之性。除却气质而单言理。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而说理较多。故不论气质。而将言修道之教。则人与人异。物与物异。故就气禀而教之也。
○尝往道峰。未至数弓许。天忽晦冥。阴云浊雨。一时四集。甚愁闷。俄而开霁。天气十分清明。因于马上思未发气质。则意思恍然开悟。以谓人之气质变化者。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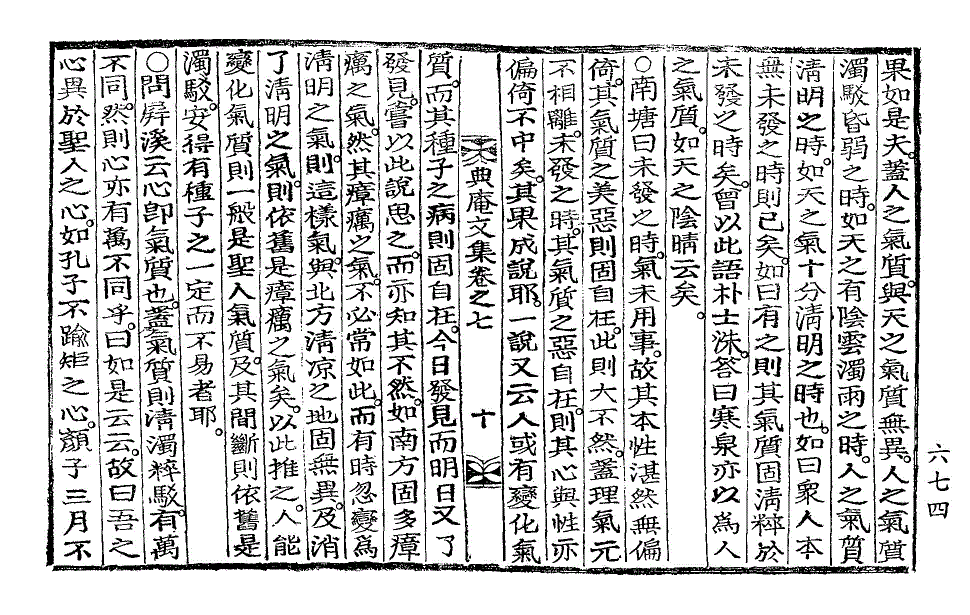 果如是夫。盖人之气质。与天之气质无异。人之气质浊驳昏弱之时。如天之有阴云浊雨之时。人之气质清明之时。如天之气十分清明之时也。如曰众人本无未发之时则已矣。如曰有之则其气质固清粹于未发之时矣。曾以此语朴士洙。答曰寒泉亦以为人之气质。如天之阴晴云矣。
果如是夫。盖人之气质。与天之气质无异。人之气质浊驳昏弱之时。如天之有阴云浊雨之时。人之气质清明之时。如天之气十分清明之时也。如曰众人本无未发之时则已矣。如曰有之则其气质固清粹于未发之时矣。曾以此语朴士洙。答曰寒泉亦以为人之气质。如天之阴晴云矣。○南塘曰未发之时。气未用事。故其本性湛然无偏倚。其气质之美恶则固自在。此则大不然。盖理气元不相离。未发之时。其气质之恶自在。则其心与性亦偏倚不中矣。其果成说耶。一说又云人或有变化气质。而其种子之病则固自在。今日发见而明日又了发见。尝以此说思之。而亦知其不然。如南方固多瘴疠之气。然其瘴疠之气。不必常如此。而有时忽变为清明之气。则这样气。与北方清凉之地固无异。及消了清明之气。则依旧是瘴疠之气矣。以此推之。人能变化气质则一般是圣人气质。及其间断则依旧是浊驳。安得有种子之一定而不易者耶。
○问屏溪云心即气质也。盖气质则清浊粹驳。有万不同。然则心亦有万不同乎。曰如是云云。故曰吾之心异于圣人之心。如孔子不踰矩之心。颜子三月不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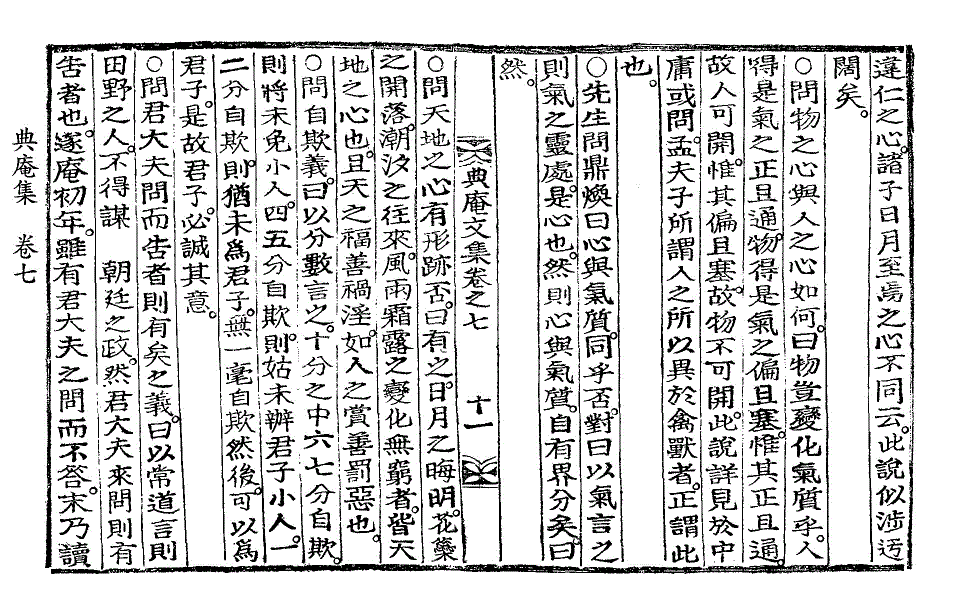 违仁之心。诸子日月至焉之心不同云。此说似涉迂阔矣。
违仁之心。诸子日月至焉之心不同云。此说似涉迂阔矣。○问物之心与人之心如何。曰物岂变化气质乎。人得是气之正且通。物得是气之偏且塞。惟其正且通。故人可开。惟其偏且塞。故物不可开。此说详见于中庸或问。孟夫子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谓此也。
○先生问鼎焕曰心与气质。同乎否。对曰以气言之则气之灵处。是心也。然则心与气质。自有界分矣。曰然。
○问天地之心有形迹否。曰有之。日月之晦明。花蕊之开落。潮汐之往来。风雨霜露之变化无穷者。皆天地之心也。且天之福善祸淫。如人之赏善罚恶也。
○问自欺义。曰以分数言之。十分之中六七分自欺。则将未免小人。四五分自欺。则姑未办君子小人。一二分自欺。则犹未为君子。无一毫自欺然后。可以为君子。是故君子。必诚其意。
○问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之义。曰以常道言则田野之人。不得谋 朝廷之政。然君大夫来问则有告者也。遂庵初年。虽有君大夫之问而不答。末乃读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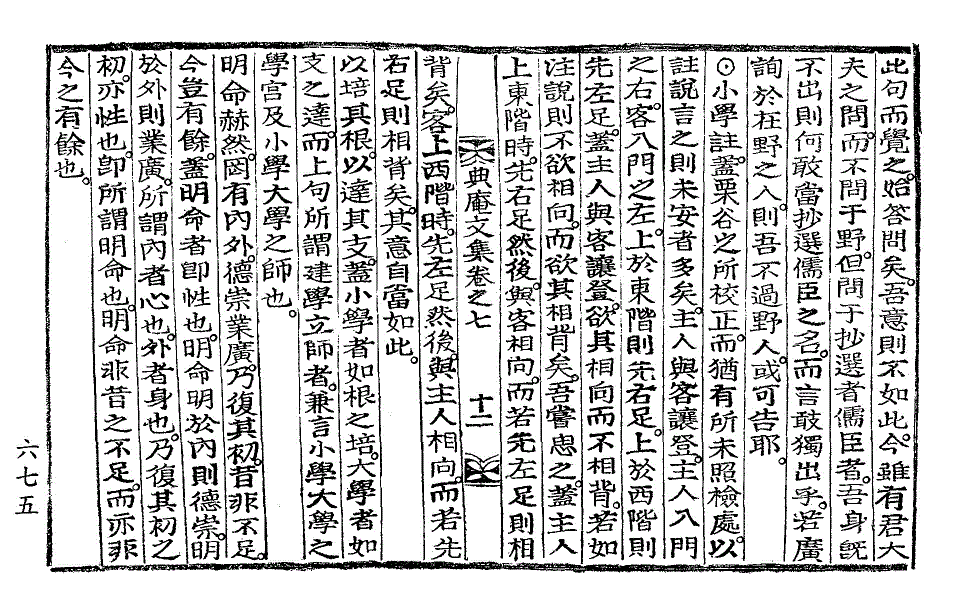 此句而觉之。始答问矣。吾意则不如此。今虽有君大夫之问。而不问于野。但问于抄选者儒臣者。吾身既不出则何敢当抄选儒臣之名。而言敢独出乎。若广询于在野之人。则吾不过野人。或可告耶。
此句而觉之。始答问矣。吾意则不如此。今虽有君大夫之问。而不问于野。但问于抄选者儒臣者。吾身既不出则何敢当抄选儒臣之名。而言敢独出乎。若广询于在野之人。则吾不过野人。或可告耶。○小学注。盖栗谷之所校正。而犹有所未照检处。以注说言之则未安者多矣。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入门之右。客入门之左。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盖主人与客让登。欲其相向而不相背。若如注说则不欲相向。而欲其相背矣。吾尝思之。盖主人上东阶时。先右足然后。与客相向。而若先左足则相背矣。客上西阶时。先左足然后。与主人相向。而若先右足则相背矣。其意自当如此。
以培其根。以达其支。盖小学者如根之培。大学者如支之达。而上句所谓建学立师者。兼言小学大学之学宫及小学大学之师也。
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业广。乃复其初。昔非不足。今岂有馀。盖明命者即性也。明命明于内则德崇。明于外则业广。所谓内者心也。外者身也。乃复其初之初。亦性也。即所谓明命也。明命非昔之不足。而亦非今之有馀也。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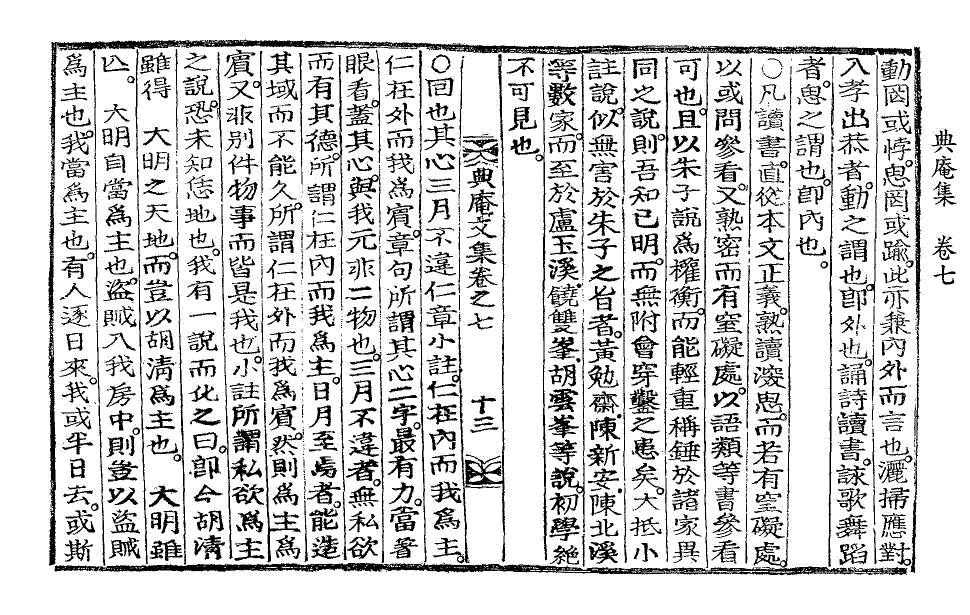 动罔或悖。思罔或踰。此亦兼内外而言也。洒扫应对。入孝出恭者。动之谓也。即外也。诵诗读书。咏歌舞蹈者。思之谓也。即内也。
动罔或悖。思罔或踰。此亦兼内外而言也。洒扫应对。入孝出恭者。动之谓也。即外也。诵诗读书。咏歌舞蹈者。思之谓也。即内也。○凡读书。直从本文正义。熟读深思。而若有窒碍处。以或问参看。又熟密而有窒碍处。以语类等书参看可也。且以朱子说为权衡。而能轻重称锤于诸家异同之说。则吾知已明。而无附会穿凿之患矣。大抵小注说。似无害于朱子之旨者。黄勉斋,陈新安,陈北溪等数家。而至于卢玉溪,饶双峰,胡云峰等说。初学绝不可见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章小注。仁在内而我为主。仁在外而我为宾。章句所谓其心二字。最有力。当著眼看。盖其心。与我元非二物也。三月不违者。无私欲而有其德。所谓仁在内而我为主。日月至焉者。能造其域而不能久。所谓仁在外而我为宾。然则为主为宾。又非别件物事而皆是我也。小注所谓私欲为主之说。恐未知恁地也。我有一说而化之曰。即今胡清虽得 大明之天地。而岂以胡清为主也。 大明虽亡。 大明自当为主也。盗贼入我房中。则岂以盗贼为主也。我当为主也。有人逐日来。我或半日去。或斯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6L 页
 须而去。岂可以半日斯须之人为主也。终日在此者。即我也。我当为主也。
须而去。岂可以半日斯须之人为主也。终日在此者。即我也。我当为主也。○余晓枕默诵中庸哀公问政章。非直义理之无穷。其文章尤善。盖此章及鬼神章。真中庸之体要也。大学传十章。出于曾子之门人。而若论门人则舍子思他求哉。吾未能质言。而疑必为子思之作也。然其文体大相不同。而大学则言学问阶梯。其题目如此。文体亦随而如此。中庸则言性与天道。其题目文体亦如此。大学中若无曾子曰字。则断然谓之曾子之作亦可也。
○鼎焕问曾见寒泉赠崔祏诗。有贻累岂不大之句。而南塘屏溪之论。则与遂庵集中语无异矣。寒泉之若此峻切何也。先生曰遂庵集虽如此。然巍岩集有与宋某人书曰。先生近改前见云。巍岩一者往见遂翁而面质曰。往者先生之言。与余吻合。今胡立异。因以其时参闻人某某證左。又阅案上朱子大全而质之。遂翁笑曰君言甚是。自此吾改前见矣。公举每以如此之说来质。甚闷矣。三渊每与我书亦如此。不胜其苦云。玄洗马亦以此等语往质。遂翁曰君辈之言性理处。我则不知所对。玄洗马历叙朱子之说而言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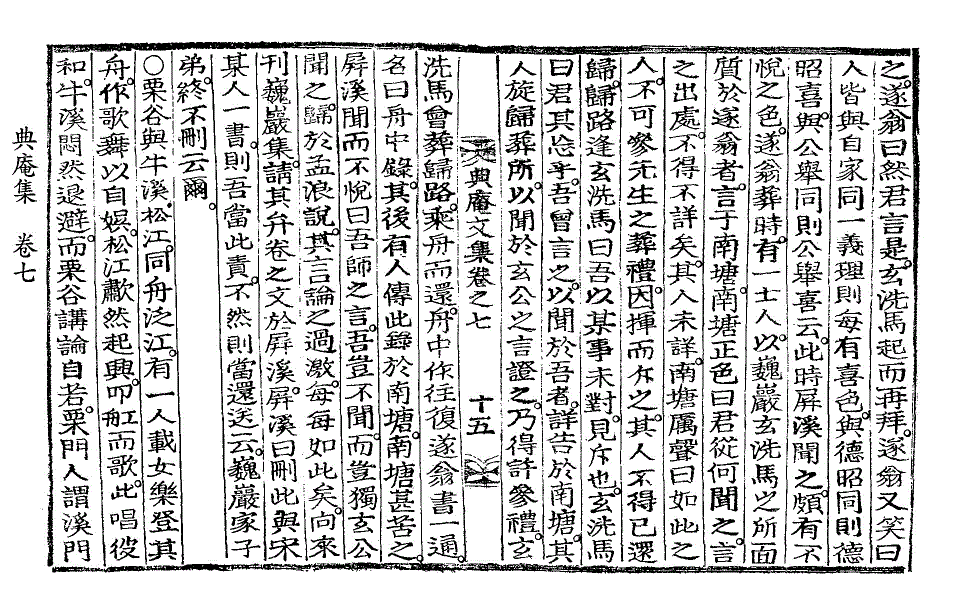 之。遂翁曰然君言是。玄洗马起而再拜。遂翁又笑曰人皆与自家同一义理则每有喜色。与德昭同则德昭喜。与公举同则公举喜云。此时屏溪闻之。颇有不悦之色。遂翁葬时。有一士人。以巍岩玄洗马之所面质于遂翁者。言于南塘。南塘正色曰君从何闻之。言之出处。不得不详矣。其人未详。南塘厉声曰如此之人。不可参先生之葬礼。因挥而斥之。其人不得已还归。归路逢玄洗马曰吾以某事未对。见斥也。玄洗马曰君其忘乎。吾曾言之。以闻于吾者。详告于南塘。其人旋归葬所。以闻于玄公之言證之。乃得许参礼。玄洗马会葬归路。乘舟而还。舟中作往复遂翁书一通。名曰舟中录。其后有人传此录于南塘。南塘甚苦之。屏溪闻而不悦曰吾师之言。吾岂不闻。而岂独玄公闻之。归于孟浪说。其言论之过激。每每如此矣。向来刊巍岩集。请其弁卷之文于屏溪。屏溪曰删此与宋某人一书。则吾当此责。不然则当还送云。巍岩家子弟。终不删云尔。
之。遂翁曰然君言是。玄洗马起而再拜。遂翁又笑曰人皆与自家同一义理则每有喜色。与德昭同则德昭喜。与公举同则公举喜云。此时屏溪闻之。颇有不悦之色。遂翁葬时。有一士人。以巍岩玄洗马之所面质于遂翁者。言于南塘。南塘正色曰君从何闻之。言之出处。不得不详矣。其人未详。南塘厉声曰如此之人。不可参先生之葬礼。因挥而斥之。其人不得已还归。归路逢玄洗马曰吾以某事未对。见斥也。玄洗马曰君其忘乎。吾曾言之。以闻于吾者。详告于南塘。其人旋归葬所。以闻于玄公之言證之。乃得许参礼。玄洗马会葬归路。乘舟而还。舟中作往复遂翁书一通。名曰舟中录。其后有人传此录于南塘。南塘甚苦之。屏溪闻而不悦曰吾师之言。吾岂不闻。而岂独玄公闻之。归于孟浪说。其言论之过激。每每如此矣。向来刊巍岩集。请其弁卷之文于屏溪。屏溪曰删此与宋某人一书。则吾当此责。不然则当还送云。巍岩家子弟。终不删云尔。○栗谷与牛溪,松江。同舟泛江。有一人载女乐登其舟。作歌舞以自娱。松江啸然起兴。叩舡而歌。此唱彼和。牛溪闷然退避。而栗谷讲论自若。栗门人谓溪门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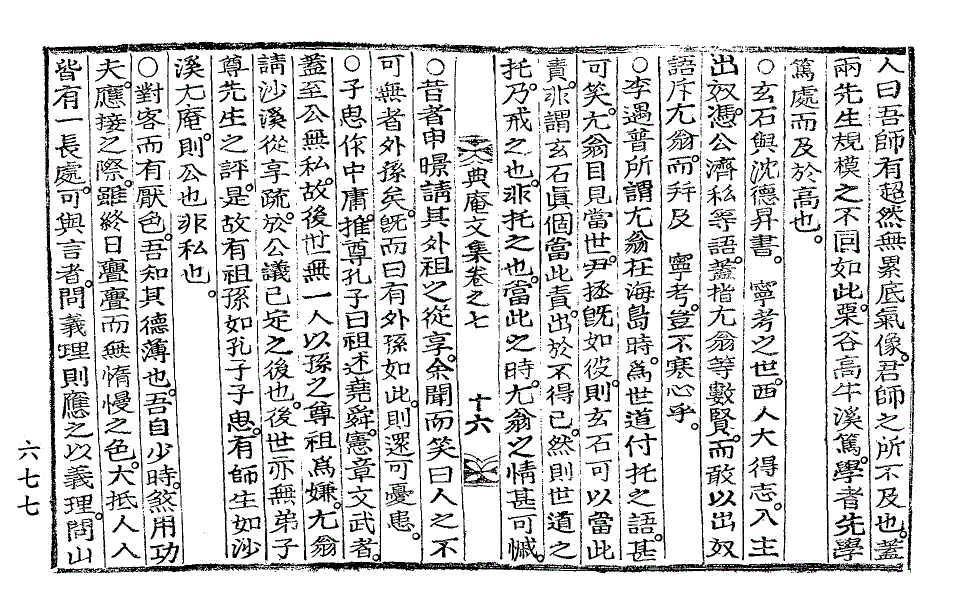 人曰吾师有超然无累底气像。君师之所不及也。盖两先生规模之不同如此。栗谷高牛溪笃。学者先学笃处而及于高也。
人曰吾师有超然无累底气像。君师之所不及也。盖两先生规模之不同如此。栗谷高牛溪笃。学者先学笃处而及于高也。○玄石与沈德升书。 宁考之世。西人大得志。入主出奴。凭公济私等语。盖指尤翁等数贤。而敢以出奴语斥尤翁。而并及 宁考。岂不寒心乎。
○李遇普所谓尤翁在海岛时。为世道付托之语。甚可笑。尤翁目见当世。尹拯既如彼。则玄石可以当此责。非谓玄石真个当此责。出于不得已。然则世道之托。乃戒之也。非托之也。当此之时。尤翁之情甚可戚。
○昔者申暻请其外祖之从享。余闻而笑曰人之不可无者外孙矣。既而曰有外孙如此。则还可忧患。
○子思作中庸。推尊孔子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盖至公无私。故后世无一人以孙之尊祖为嫌。尤翁请沙溪从享疏。于公议已定之后也。后世亦无弟子尊先生之评。是故有祖孙如孔子子思。有师生如沙溪尤庵。则公也非私也。
○对客而有厌色。吾知其德薄也。吾自少时。煞用功夫。应接之际。虽终日亹亹而无惰慢之色。大抵人人皆有一长处。可与言者。问义理则应之以义理。问山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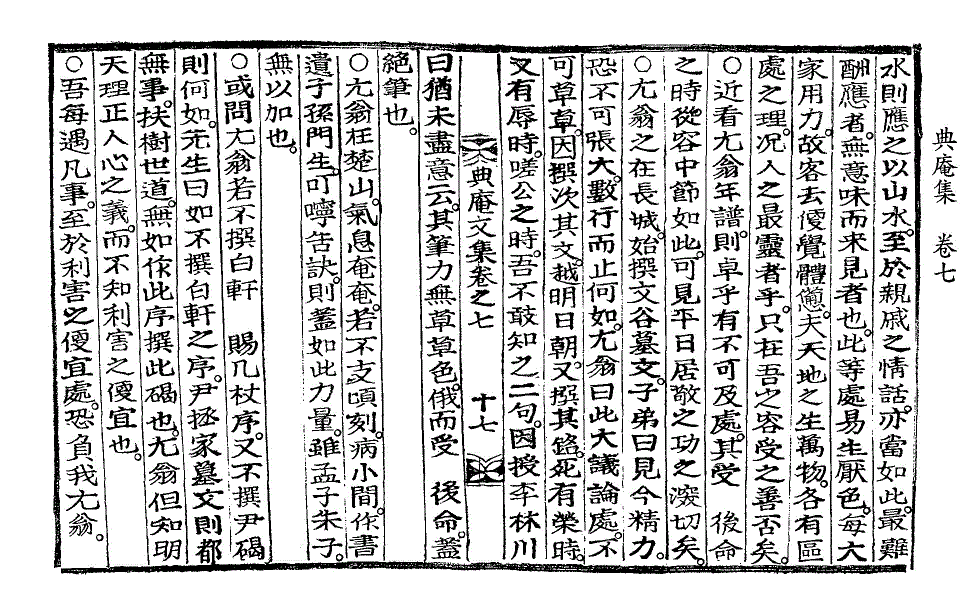 水则应之以山水。至于亲戚之情话。亦当如此。最难酬应者。无意味而来见者也。此等处易生厌色。每大家用力。故客去便觉体惫。夫天地之生万物。各有区处之理。况人之最灵者乎。只在吾之容受之善否矣。
水则应之以山水。至于亲戚之情话。亦当如此。最难酬应者。无意味而来见者也。此等处易生厌色。每大家用力。故客去便觉体惫。夫天地之生万物。各有区处之理。况人之最灵者乎。只在吾之容受之善否矣。○近看尤翁年谱。则卓乎有不可及处。其受 后命之时。从容中节如此。可见平日居敬之功之深切矣。
○尤翁之在长城。始撰文谷墓文。子弟曰见今精力。恐不可张大。数行而止何如。尤翁曰此大议论处。不可草草。因撰次其文。越明日朝。又撰其铭。死有荣时。又有辱时。嗟公之时。吾不敢知之二句。因授李林川曰犹未尽意云。其笔力无草草色。俄而受 后命。盖绝笔也。
○尤翁在楚山。气息奄奄。若不支顷刻。病小间。作书遗子孙门生。叮咛告诀。则盖如此力量。虽孟子朱子。无以加也。
○或问尤翁若不撰白轩 赐几杖序。又不撰尹碣则何如。先生曰如不撰白轩之序。尹拯家墓文则都无事。扶树世道。无如作此序撰此碣也。尤翁但知明天理正人心之义。而不知利害之便宜也。
○吾每遇凡事。至于利害之便宜处。恐负我尤翁。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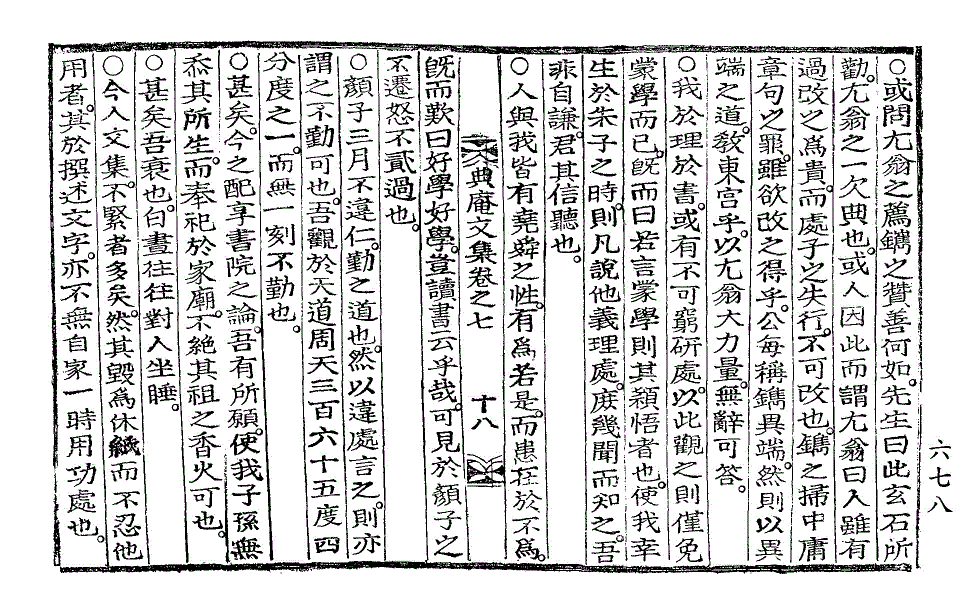 ○或问尤翁之荐镌之赞善何如。先生曰此玄石所劝。尤翁之一欠典也。或人因此而谓尤翁曰人虽有过改之为贵。而处子之失行。不可改也。镌(一作鑴)之扫中庸章句之罪。虽欲改之得乎。公每称镌(一作鑴)异端。然则以异端之道。教东宫乎。以尤翁大力量。无辞可答。
○或问尤翁之荐镌之赞善何如。先生曰此玄石所劝。尤翁之一欠典也。或人因此而谓尤翁曰人虽有过改之为贵。而处子之失行。不可改也。镌(一作鑴)之扫中庸章句之罪。虽欲改之得乎。公每称镌(一作鑴)异端。然则以异端之道。教东宫乎。以尤翁大力量。无辞可答。○我于理于书。或有不可穷研处。以此观之则仅免蒙学而已。既而曰若言蒙学则其颖悟者也。使我幸生于朱子之时。则凡说他义理处。庶几闻而知之。吾非自谦。君其信听也。
○人与我皆有尧舜之性。有为若是。而患在于不为。既而叹曰好学好学。岂读书云乎哉。可见于颜子之不迁怒不贰过也。
○颜子三月不违仁。勤之道也。然以违处言之。则亦谓之不勤可也。吾观于天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无一刻不勤也。
○甚矣。今之配享书院之论。吾有所愿。使我子孙无忝其所生。而奉祀于家庙。不绝其祖之香火可也。
○甚矣吾衰也。白昼往往对人坐睡。
○今人文集。不紧者多矣。然其毁为休纸而不忍他用者。其于撰述文字。亦不无自家一时用功处也。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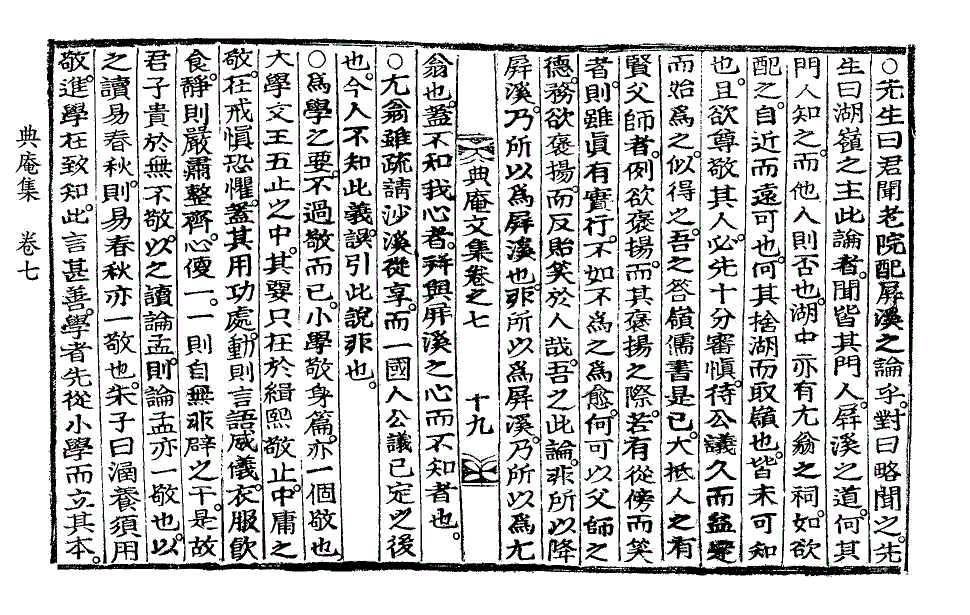 ○先生曰君闻老院配屏溪之论乎。对曰略闻之。先生曰湖岭之主此论者。闻皆其门人。屏溪之道。何其门人知之。而他人则否也。湖中亦有尤翁之祠。如欲配之。自近而远可也。何其舍湖而取岭也。皆未可知也。且欲尊敬其人。必先十分审慎。待公议久而益定而始为之。似得之。吾之答岭儒书是已。大抵人之有贤父师者。例欲褒扬。而其褒扬之际。若有从傍而笑者。则虽真有实行。不如不为之为愈。何可以父师之德。务欲褒扬。而反贻笑于人哉。吾之此论。非所以降屏溪。乃所以为屏溪也。非所以为屏溪。乃所以为尤翁也。盖不知我心者。并与屏溪之心而不知者也。
○先生曰君闻老院配屏溪之论乎。对曰略闻之。先生曰湖岭之主此论者。闻皆其门人。屏溪之道。何其门人知之。而他人则否也。湖中亦有尤翁之祠。如欲配之。自近而远可也。何其舍湖而取岭也。皆未可知也。且欲尊敬其人。必先十分审慎。待公议久而益定而始为之。似得之。吾之答岭儒书是已。大抵人之有贤父师者。例欲褒扬。而其褒扬之际。若有从傍而笑者。则虽真有实行。不如不为之为愈。何可以父师之德。务欲褒扬。而反贻笑于人哉。吾之此论。非所以降屏溪。乃所以为屏溪也。非所以为屏溪。乃所以为尤翁也。盖不知我心者。并与屏溪之心而不知者也。○尤翁虽疏请沙溪从享。而一国人公议已定之后也。今人不知此义。误引此说非也。
○为学之要。不过敬而已。小学敬身篇。亦一个敬也。大学文王五止之中。其要只在于缉熙敬止。中庸之敬。在戒慎恐惧。盖其用功处。动则言语威仪。衣服饮食。静则严肃整齐。心便一。一则自无非辟之干。是故君子贵于无不敬。以之读论孟。则论孟亦一敬也。以之读易春秋。则易春秋亦一敬也。朱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言甚善。学者先从小学而立其本。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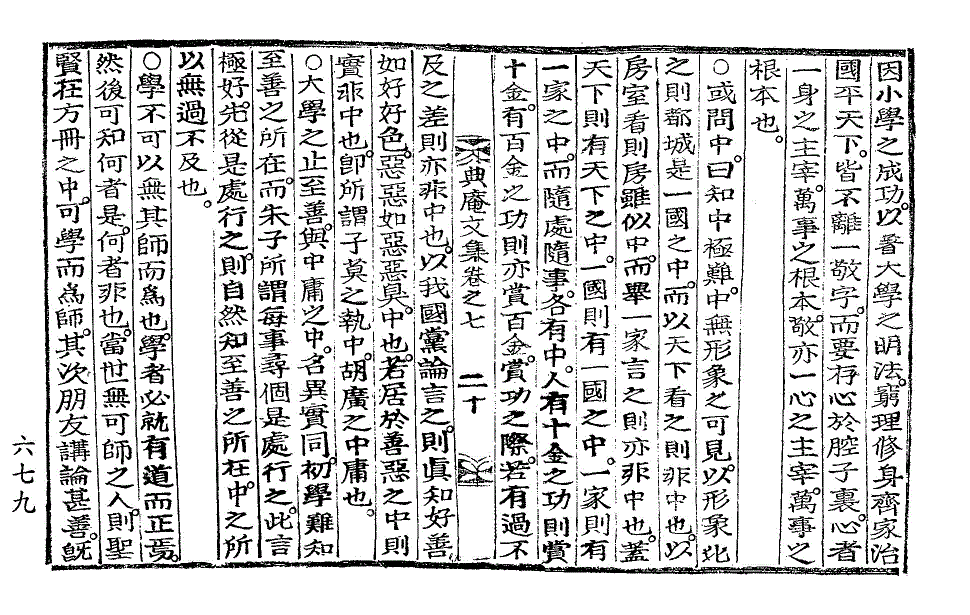 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离一敬字。而要存心于腔子里。心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敬亦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也。
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离一敬字。而要存心于腔子里。心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根本。敬亦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也。○或问中。曰知中极难。中无形象之可见。以形象比之则都城是一国之中。而以天下看之则非中也。以房室看则房虽似中。而举一家言之则亦非中也。盖天下则有天下之中。一国则有一国之中。一家则有一家之中。而随处随事。各有中。人有十金之功则赏十金。有百金之功则亦赏百金。赏功之际。若有过不及之差则亦非中也。以我国党论言之。则真知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中也。若居于善恶之中则实非中也。即所谓子莫之执中。胡广之中庸也。
○大学之止至善。与中庸之中。名异实同。初学难知至善之所在。而朱子所谓每事寻个是处行之。此言极好。先从是处行之。则自然知至善之所在。中之所以无过不及也。
○学不可以无其师而为也。学者必就有道而正焉。然后可知何者是。何者非也。当世无可师之人。则圣贤在方册之中。可学而为师。其次朋友讲论甚善。既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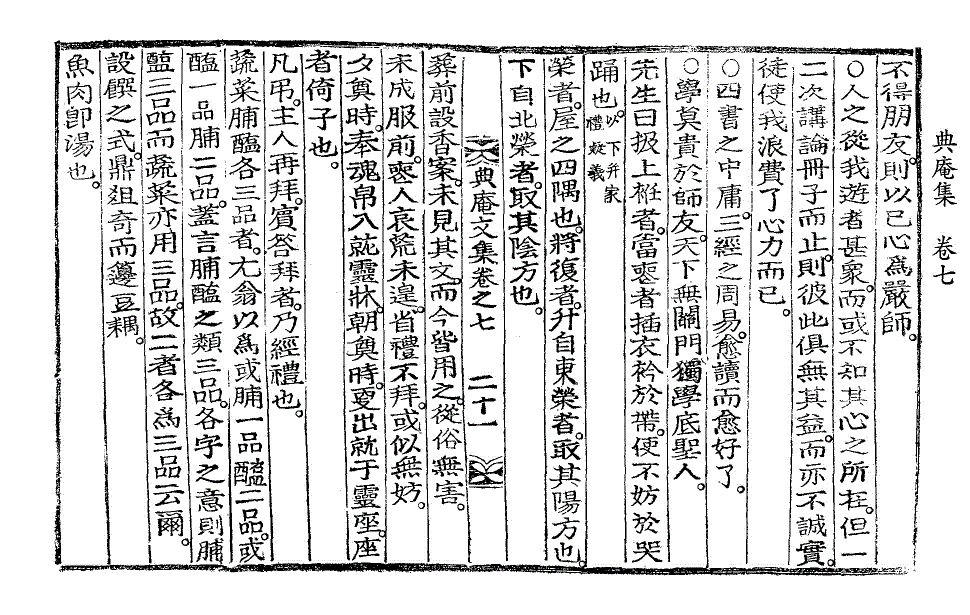 不得朋友。则以己心为严师。
不得朋友。则以己心为严师。○人之从我游者甚众。而或不知其心之所在。但一二次讲论册子而止。则彼此俱无其益。而亦不诚实。徒使我浪费了心力而已。
○四书之中庸。三经之周易。愈读而愈好了。
○学莫贵于师友。天下无关门独学底圣人。
先生曰扱上衽者。当丧者插衣衿于带。使不妨于哭踊也。(以下并家礼疑义。)
荣者。屋之四隅也。将复者。升自东荣者。取其阳方也。下自北荣者。取其阴方也。
葬前设香案。未见其文。而今皆用之。从俗无害。
未成服前。丧人哀荒未遑。省礼不拜。或似无妨。
夕奠时。奉魂帛入就灵床。朝奠时。更出就于灵座。座者倚子也。
凡吊。主人再拜。宾答拜者。乃经礼也。
蔬菜脯醢各三品者。尤翁以为或脯一品醢二品。或醢一品脯二品。盖言脯醢之类三品。各字之意则脯醢三品而蔬菜亦用三品。故二者各为三品云尔。
设馔之式。鼎俎奇而笾豆耦。
鱼肉即汤也。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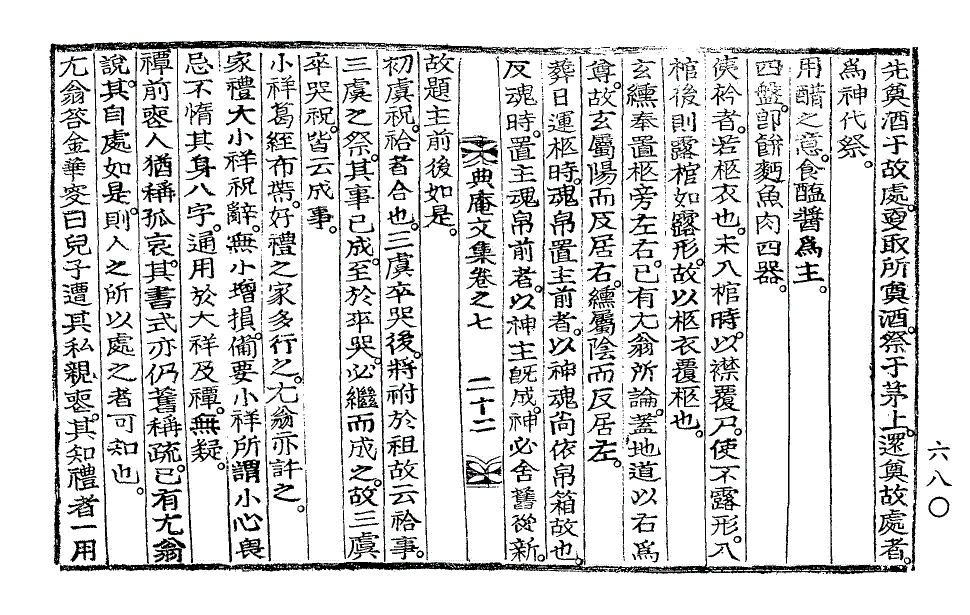 先奠酒于故处。更取所奠酒。祭于茅上。还奠故处者。为神代祭。
先奠酒于故处。更取所奠酒。祭于茅上。还奠故处者。为神代祭。用醋之意。食醢酱为主。
四盘。即饼面鱼肉四器。
侇衿者。若柩衣也。未入棺时。以襟覆尸。使不露形。入棺后则露棺如露形。故以柩衣覆柩也。
玄纁奉置柩旁左右。已有尤翁所论。盖地道以右为尊。故玄属阳而反居右。纁属阴而反居左。
葬日运柩时。魂帛置主前者。以神魂尚依帛箱故也。反魂时。置主魂帛前者。以神主既成。神必舍旧从新。故题主前后如是。
初虞祝。祫者合也。三虞卒哭后。将祔于祖故云祫事。三虞之祭。其事已成。至于卒哭。必继而成之。故三虞卒哭祝。皆云成事。
小祥葛绖布带。好礼之家多行之。尤翁亦许之。
家礼大小祥祝辞。无小增损。备要小祥所谓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通用于大祥及禫。无疑。
禫前丧人犹称孤哀。其书式亦仍旧称疏。已有尤翁说。其自处如是。则人之所以处之者可知也。
尤翁答金华叟曰儿子遭其私亲丧。其知礼者一用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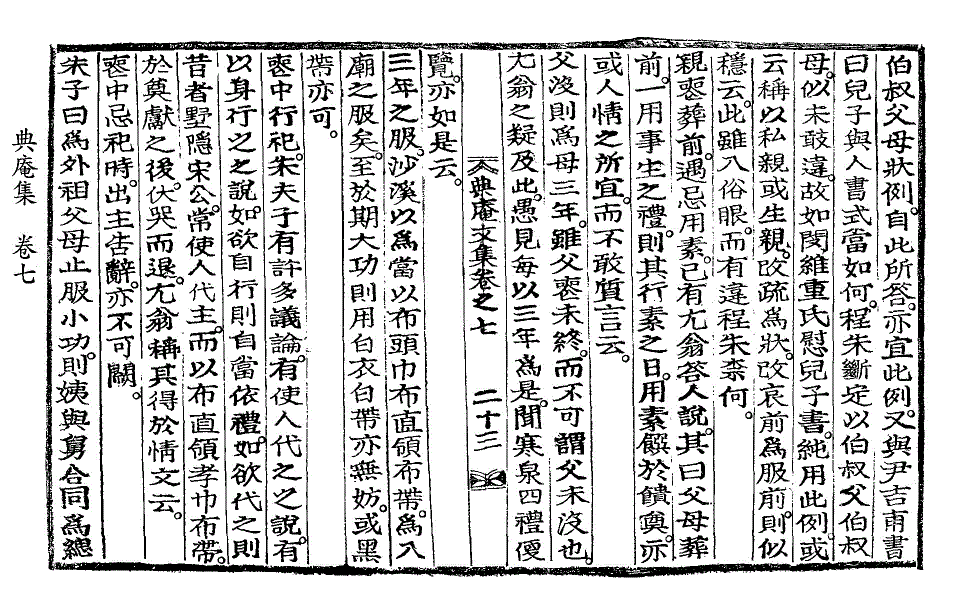 伯叔父母状例。自此所答。亦宜此例。又与尹吉甫书曰儿子与人书式当如何。程朱断定以伯叔父伯叔母。似未敢违。故如闵维重氏慰儿子书。纯用此例。或云称以私亲或生亲。改疏为状。改哀前为服前。则似稳云。此虽入俗眼。而有违程朱柰何。
伯叔父母状例。自此所答。亦宜此例。又与尹吉甫书曰儿子与人书式当如何。程朱断定以伯叔父伯叔母。似未敢违。故如闵维重氏慰儿子书。纯用此例。或云称以私亲或生亲。改疏为状。改哀前为服前。则似稳云。此虽入俗眼。而有违程朱柰何。亲丧葬前。遇忌用素。已有尤翁答人说。其曰父母葬前。一用事生之礼。则其行素之日。用素馔于馈奠。亦或人情之所宜。而不敢质言云。
父没则为母三年。虽父丧未终。而不可谓父未没也。尤翁之疑及此。愚见每以三年为是。闻寒泉四礼便览。亦如是云。
三年之服。沙溪以为当以布头巾布直领布带。为入庙之服矣。至于期大功则用白衣白带亦无妨。或黑带亦可。
丧中行祀。朱夫子有许多议论。有使人代之之说。有以身行之之说。如欲自行则自当依礼。如欲代之则昔者墅隐宋公。常使人代主。而以布直领孝巾布带。于奠献之后。伏哭而退。尤翁称其得于情文云。
丧中忌祀时。出主告辞。亦不可阙。
朱子曰为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则姨与舅合同为缌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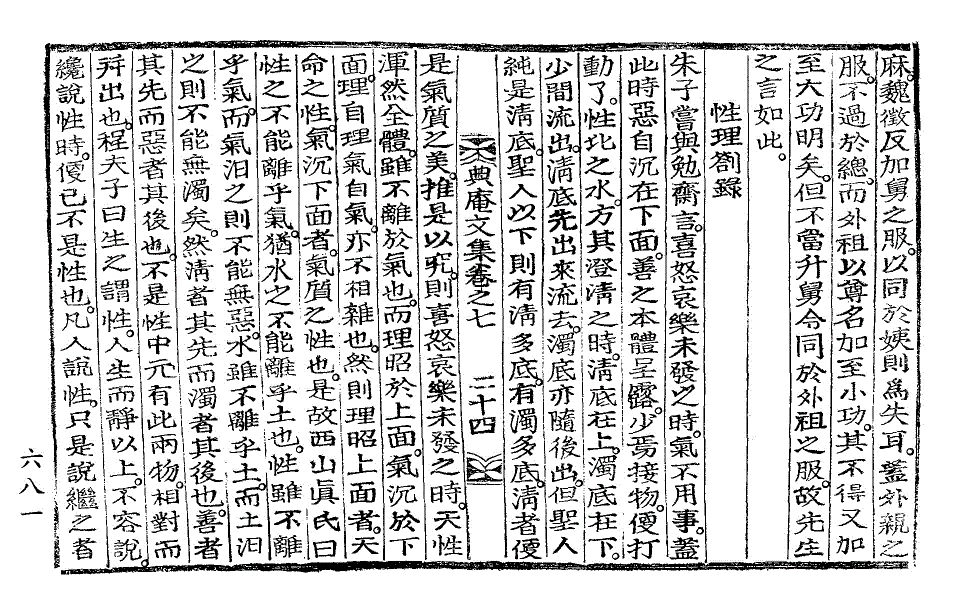 麻。魏徵反加舅之服。以同于姨则为失耳。盖外亲之服。不过于缌。而外祖以尊名加至小功。其不得又加至大功明矣。但不当升舅令同于外祖之服。故先生之言如此。
麻。魏徵反加舅之服。以同于姨则为失耳。盖外亲之服。不过于缌。而外祖以尊名加至小功。其不得又加至大功明矣。但不当升舅令同于外祖之服。故先生之言如此。性理劄录
朱子尝与勉斋言。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不用事。盖此时恶自沉在下面。善之本体呈露。少焉接物。便打动了。性比之水。方其澄清之时。清底在上。浊底在下。少间流出。清底先出来流去。浊底亦随后出。但圣人纯是清底。圣人以下则有清多底。有浊多底。清者便是气质之美。推是以究。则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天性浑然全体。虽不离于气也。而理昭于上面。气沉于下面。理自理气自气。亦不相杂也。然则理昭上面者。天命之性。气沉下面者。气质之性也。是故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离乎气。犹水之不能离乎土也。性虽不离乎气。而气汩之则不能无恶。水虽不离乎土。而土汩之则不能无浊矣。然清者其先而浊者其后也。善者其先而恶者其后也。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并出也。程夫子曰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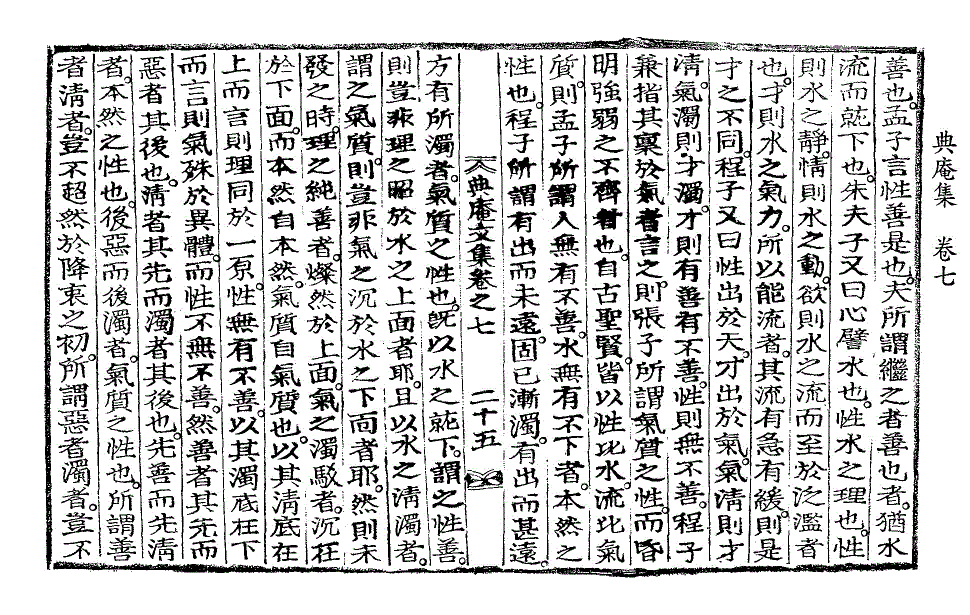 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朱夫子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则水之静。情则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泛滥者也。才则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程子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张子所谓气质之性。而昏明强弱之不齐者也。自古圣贤。皆以性比水。流比气质。则孟子所谓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者。本然之性也。程子所谓有出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者。气质之性也。既以水之就下。谓之性善。则岂非理之昭于水之上面者耶。且以水之清浊者。谓之气质。则岂非气之沉于水之下面者耶。然则未发之时。理之纯善者。灿然于上面。气之浊驳者。沉在于下面。而本然自本然。气质自气质也。以其清底在上而言则理同于一原。性无有不善。以其浊底在下而言则气殊于异体。而性不无不善。然善者其先而恶者其后也。清者其先而浊者其后也。先善而先清者。本然之性也。后恶而后浊者。气质之性也。所谓善者清者。岂不超然于降衷之初。所谓恶者浊者。岂不
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朱夫子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则水之静。情则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泛滥者也。才则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程子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张子所谓气质之性。而昏明强弱之不齐者也。自古圣贤。皆以性比水。流比气质。则孟子所谓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者。本然之性也。程子所谓有出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者。气质之性也。既以水之就下。谓之性善。则岂非理之昭于水之上面者耶。且以水之清浊者。谓之气质。则岂非气之沉于水之下面者耶。然则未发之时。理之纯善者。灿然于上面。气之浊驳者。沉在于下面。而本然自本然。气质自气质也。以其清底在上而言则理同于一原。性无有不善。以其浊底在下而言则气殊于异体。而性不无不善。然善者其先而恶者其后也。清者其先而浊者其后也。先善而先清者。本然之性也。后恶而后浊者。气质之性也。所谓善者清者。岂不超然于降衷之初。所谓恶者浊者。岂不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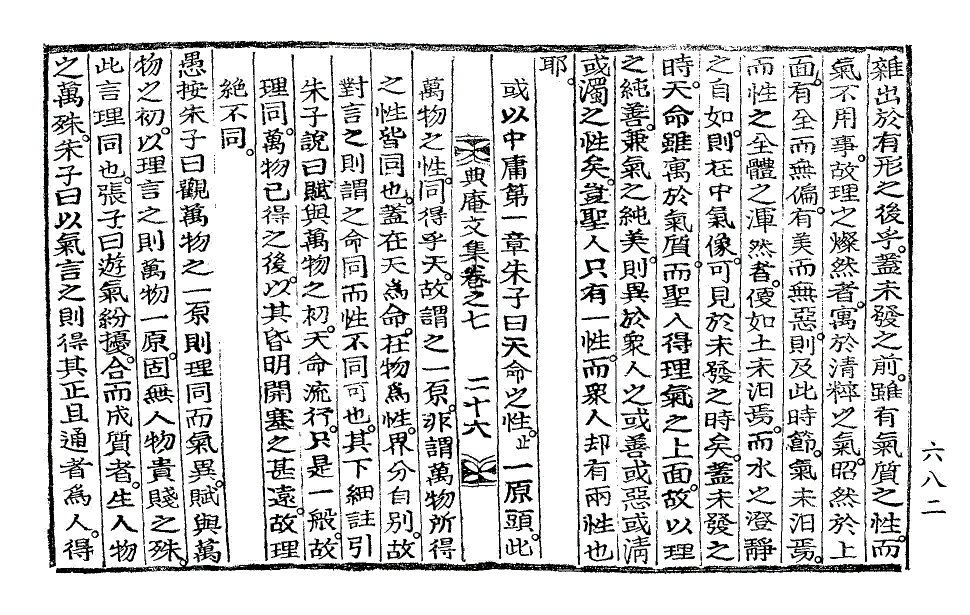 杂出于有形之后乎。盖未发之前。虽有气质之性。而气不用事。故理之灿然者。寓于清粹之气。昭然于上面。有全而无偏。有美而无恶。则及此时节。气未汩焉。而性之全体之浑然者。便如土未汩焉。而水之澄静之自如。则在中气像。可见于未发之时矣。盖未发之时。天命虽寓于气质。而圣人得理气之上面。故以理之纯善。兼气之纯美。则异于众人之或善或恶或清或浊之性矣。岂圣人只有一性。而众人却有两性也耶。
杂出于有形之后乎。盖未发之前。虽有气质之性。而气不用事。故理之灿然者。寓于清粹之气。昭然于上面。有全而无偏。有美而无恶。则及此时节。气未汩焉。而性之全体之浑然者。便如土未汩焉。而水之澄静之自如。则在中气像。可见于未发之时矣。盖未发之时。天命虽寓于气质。而圣人得理气之上面。故以理之纯善。兼气之纯美。则异于众人之或善或恶或清或浊之性矣。岂圣人只有一性。而众人却有两性也耶。或以中庸第一章朱子曰天命之性。(止。)一原头。此万物之性。同得乎天。故谓之一原。非谓万物所得之性皆同也。盖在天为命。在物为性。界分自别。故对言之则谓之命同而性不同可也。其下细注引朱子说曰赋与万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万物已得之后。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
愚按朱子曰观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赋与万物之初。以理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此言理同也。张子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朱子曰以气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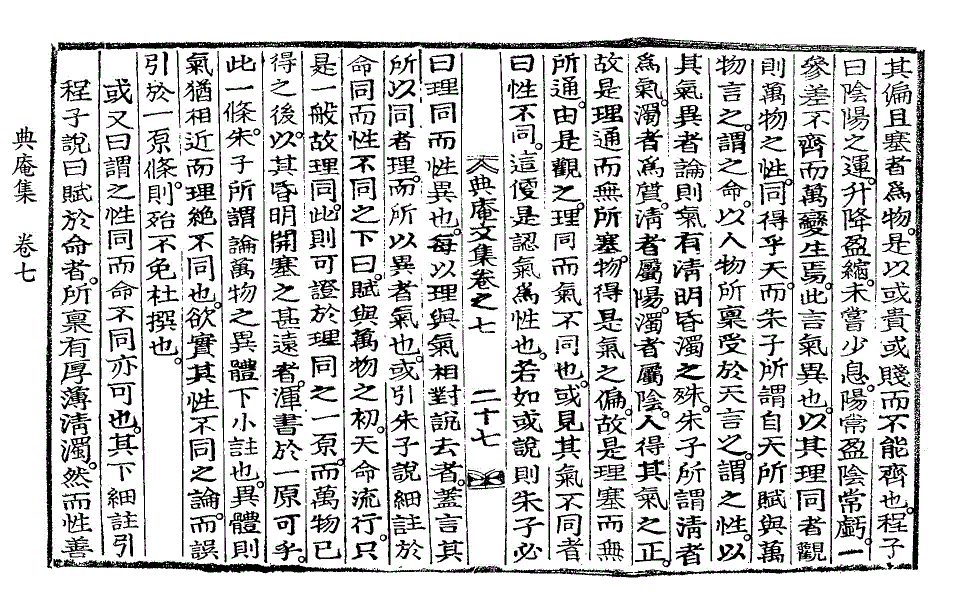 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程子曰阴阳之运。升降盈缩。未尝少息。阳常盈阴常亏。一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此言气异也。以其理同者观则万物之性。同得乎天。而朱子所谓自天所赋与万物言之。谓之命。以人物所禀受于天言之。谓之性。以其气异者论则气有清明昏浊之殊。朱子所谓清者为气。浊者为质。清者属阳。浊者属阴。人得其气之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是气之偏。故是理塞而无所通。由是观之。理同而气不同也。或见其气不同者曰性不同。这便是认气为性也。若如或说则朱子必曰理同而性异也。每以理与气相对说去者。盖言其所以同者理。而所以异者气也。或引朱子说细注于命同而性不同之下曰。赋与万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此则可證于理同之一原。而万物已得之后。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者。浑书于一原可乎。此一条。朱子所谓论万物之异体下小注也。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欲实其性不同之论。而误引于一原条。则殆不免杜撰也。
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程子曰阴阳之运。升降盈缩。未尝少息。阳常盈阴常亏。一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此言气异也。以其理同者观则万物之性。同得乎天。而朱子所谓自天所赋与万物言之。谓之命。以人物所禀受于天言之。谓之性。以其气异者论则气有清明昏浊之殊。朱子所谓清者为气。浊者为质。清者属阳。浊者属阴。人得其气之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是气之偏。故是理塞而无所通。由是观之。理同而气不同也。或见其气不同者曰性不同。这便是认气为性也。若如或说则朱子必曰理同而性异也。每以理与气相对说去者。盖言其所以同者理。而所以异者气也。或引朱子说细注于命同而性不同之下曰。赋与万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此则可證于理同之一原。而万物已得之后。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者。浑书于一原可乎。此一条。朱子所谓论万物之异体下小注也。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欲实其性不同之论。而误引于一原条。则殆不免杜撰也。或又曰谓之性同而命不同亦可也。其下细注引程子说曰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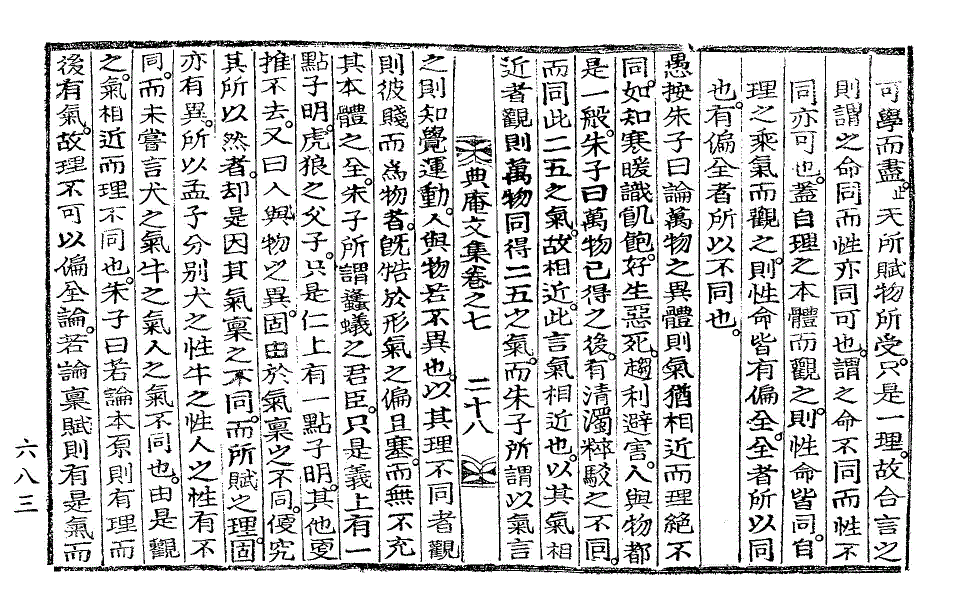 可学而尽。(止。)天所赋物所受。只是一理。故合言之则谓之命同而性亦同可也。谓之命不同而性不同亦可也。盖自理之本体而观之。则性命皆同。自理之乘气而观之。则性命皆有偏全。全者所以同也。有偏全者所以不同也。
可学而尽。(止。)天所赋物所受。只是一理。故合言之则谓之命同而性亦同可也。谓之命不同而性不同亦可也。盖自理之本体而观之。则性命皆同。自理之乘气而观之。则性命皆有偏全。全者所以同也。有偏全者所以不同也。愚按朱子曰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如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是一般。朱子曰万物已得之后。有清浊粹驳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相近。此言气相近也。以其气相近者观则万物同得二五之气。而朱子所谓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其理不同者观则彼贱而为物者。既牿于形气之偏且塞。而无不充其本体之全。朱子所谓蜂蚁之君臣。只是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又曰人与物之异。固由于气禀之不同。便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气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而未尝言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不同也。由是观之。气相近而理不同也。朱子曰若论本原则有理而后有气。故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禀赋则有是气而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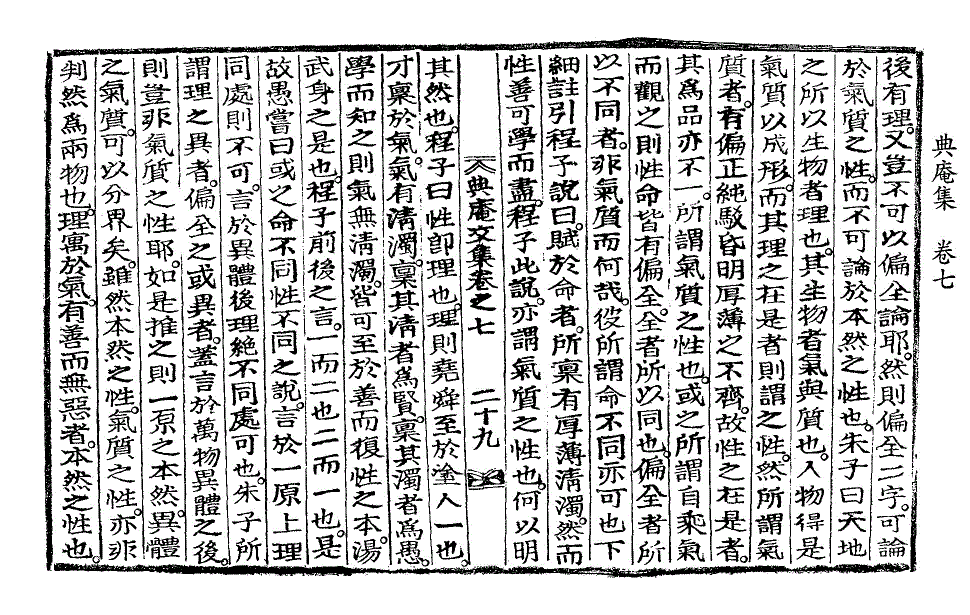 后有理。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然则偏全二字。可论于气质之性。而不可论于本然之性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然所谓气质者。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所谓气质之性也。或之所谓自乘气而观之则性命皆有偏全。全者所以同也。偏全者所以不同者。非气质而何哉。彼所谓命不同亦可也下细注引程子说曰。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程子此说。亦谓气质之性也。何以明其然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程子前后之言。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是故愚尝曰或之命不同性不同之说。言于一原上理同处则不可。言于异体后理绝不同处可也。朱子所谓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者。盖言于万物异体之后。则岂非气质之性耶。如是推之则一原之本然。异体之气质。可以分界矣。虽然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亦非判然为两物也。理寓于气。有善而无恶者。本然之性也。
后有理。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然则偏全二字。可论于气质之性。而不可论于本然之性也。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然所谓气质者。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所谓气质之性也。或之所谓自乘气而观之则性命皆有偏全。全者所以同也。偏全者所以不同者。非气质而何哉。彼所谓命不同亦可也下细注引程子说曰。赋于命者。所禀有厚薄清浊。然而性善可学而尽。程子此说。亦谓气质之性也。何以明其然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程子前后之言。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是故愚尝曰或之命不同性不同之说。言于一原上理同处则不可。言于异体后理绝不同处可也。朱子所谓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者。盖言于万物异体之后。则岂非气质之性耶。如是推之则一原之本然。异体之气质。可以分界矣。虽然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亦非判然为两物也。理寓于气。有善而无恶者。本然之性也。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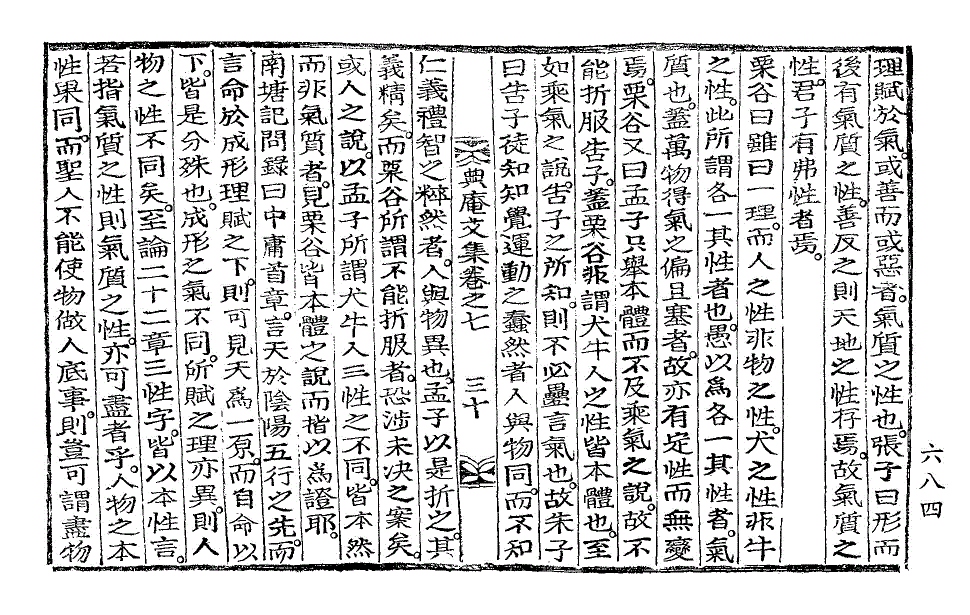 理赋于气。或善而或恶者。气质之性也。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理赋于气。或善而或恶者。气质之性也。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栗谷曰虽曰一理。而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谓各一其性者也。愚以为各一其性者。气质也。盖万物得气之偏且塞者。故亦有定性而无变焉。栗谷又曰孟子只举本体而不及乘气之说。故不能折服告子。盖栗谷非谓犬牛人之性皆本体也。至如乘气之说。告子之所知。则不必叠言气也。故朱子曰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而栗谷所谓不能折服者。恐涉未决之案矣。或人之说。以孟子所谓犬牛人三性之不同。皆本然而非气质者。见栗谷皆本体之说而指以为證耶。
南塘记问录曰中庸首章。言天于阴阳五行之先。而言命于成形理赋之下。则可见天为一原。而自命以下。皆是分殊也。成形之气不同。所赋之理亦异。则人物之性不同矣。至论二十二章三性字。皆以本性言。若指气质之性则气质之性。亦可尽者乎。人物之本性果同。而圣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则岂可谓尽物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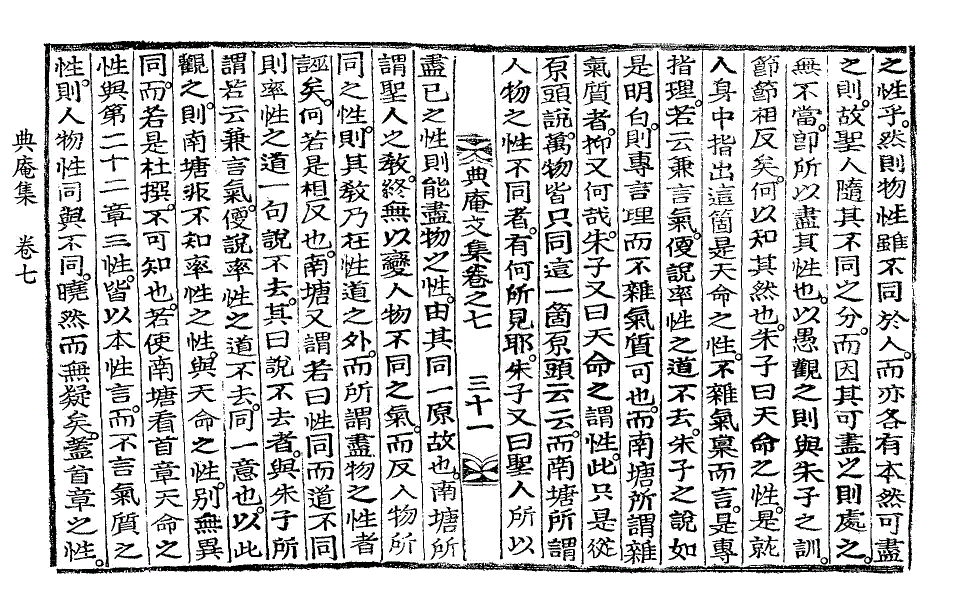 之性乎。然则物性虽不同于人。而亦各有本然可尽之则。故圣人随其不同之分。而因其可画之则处之。无不当。即所以尽其性也。以愚观之则与朱子之训。节节相反矣。何以知其然也。朱子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是专指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朱子之说如是明白。则专言理而不杂气质可也。而南塘所谓杂气质者。抑又何哉。朱子又曰天命之谓性。此只是从原头说。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云云。而南塘所谓人物之性不同者。有何所见耶。朱子又曰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南塘所谓圣人之教。终无以变人物不同之气。而反人物所同之性。则其教乃在性道之外。而所谓尽物之性者诬矣。何若是相反也。南塘又谓若曰性同而道不同则率性之道一句说不去。其曰说不去者。与朱子所谓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同一意也。以此观之。则南塘非不知率性之性。与天命之性。别无异同。而若是杜撰。不可知也。若使南塘看首章天命之性与第二十二章三性。皆以本性言。而不言气质之性。则人物性同与不同。晓然而无疑矣。盖首章之性。
之性乎。然则物性虽不同于人。而亦各有本然可尽之则。故圣人随其不同之分。而因其可画之则处之。无不当。即所以尽其性也。以愚观之则与朱子之训。节节相反矣。何以知其然也。朱子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是专指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朱子之说如是明白。则专言理而不杂气质可也。而南塘所谓杂气质者。抑又何哉。朱子又曰天命之谓性。此只是从原头说。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云云。而南塘所谓人物之性不同者。有何所见耶。朱子又曰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南塘所谓圣人之教。终无以变人物不同之气。而反人物所同之性。则其教乃在性道之外。而所谓尽物之性者诬矣。何若是相反也。南塘又谓若曰性同而道不同则率性之道一句说不去。其曰说不去者。与朱子所谓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同一意也。以此观之。则南塘非不知率性之性。与天命之性。别无异同。而若是杜撰。不可知也。若使南塘看首章天命之性与第二十二章三性。皆以本性言。而不言气质之性。则人物性同与不同。晓然而无疑矣。盖首章之性。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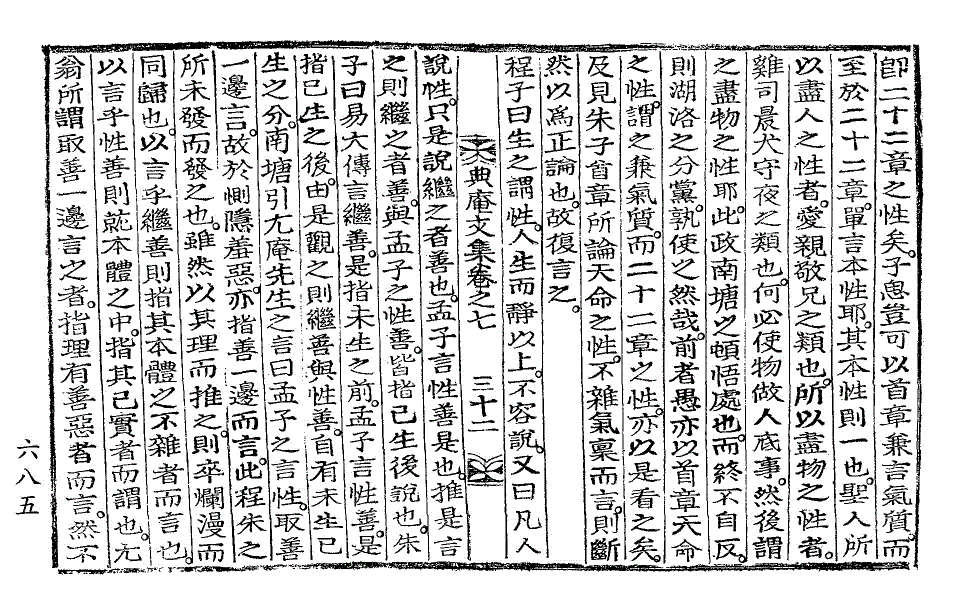 即二十二章之性矣。子思岂可以首章兼言气质。而至于二十二章。单言本性耶。其本性则一也。圣人所以尽人之性者。爱亲敬兄之类也。所以尽物之性者。鸡司晨犬守夜之类也。何必使物做人底事。然后谓之尽物之性耶。此政南塘之顿悟处也。而终不自反。则湖洛之分党。孰使之然哉。前者愚亦以首章天命之性。谓之兼气质。而二十二章之性。亦以是看之矣。及见朱子首章所论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则断然以为正论也。故复言之。
即二十二章之性矣。子思岂可以首章兼言气质。而至于二十二章。单言本性耶。其本性则一也。圣人所以尽人之性者。爱亲敬兄之类也。所以尽物之性者。鸡司晨犬守夜之类也。何必使物做人底事。然后谓之尽物之性耶。此政南塘之顿悟处也。而终不自反。则湖洛之分党。孰使之然哉。前者愚亦以首章天命之性。谓之兼气质。而二十二章之性。亦以是看之矣。及见朱子首章所论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则断然以为正论也。故复言之。程子曰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又曰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推是言之则继之者善。与孟子之性善。皆指已生后说也。朱子曰易大传言继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由是观之则继善与性善。自有未生已生之分。南塘引尤庵先生之言曰孟子之言性。取善一边言。故于恻隐羞恶。亦指善一边而言。此程朱之所未发而发之也。虽然以其理而推之。则卒烂漫而同归也。以言乎继善则指其本体之不杂者而言也。以言乎性善则就本体之中。指其已实者而谓也。尤翁所谓取善一边言之者。指理有善恶者而言。然不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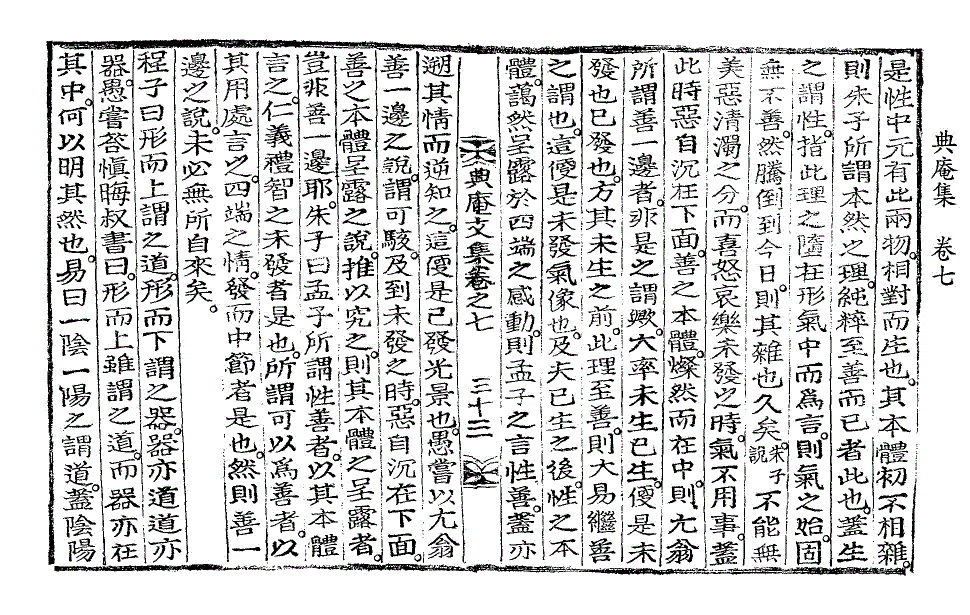 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其本体初不相杂。则朱子所谓本然之理。纯粹至善而已者此也。盖生之谓性。指此理之堕在形气中而为言。则气之始。固无不善。然腾倒到今日。则其杂也久矣。(朱子说。)不能无美恶清浊之分。而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不用事。盖此时恶自沉在下面。善之本体。灿然而在中。则尤翁所谓善一边者。非是之谓欤。大率未生已生。便是未发也已发也。方其未生之前。此理至善。则大易继善之谓也。这便是未发气像也。及夫已生之后。性之本体。蔼然呈露于四端之感动。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这便是已发光景也。愚尝以尤翁善一边之说。谓可骇。及到未发之时。恶自沉在下面。善之本体呈露之说。推以究之。则其本体之呈露者。岂非善一边耶。朱子曰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然则善一边之说。未必无所自来矣。
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其本体初不相杂。则朱子所谓本然之理。纯粹至善而已者此也。盖生之谓性。指此理之堕在形气中而为言。则气之始。固无不善。然腾倒到今日。则其杂也久矣。(朱子说。)不能无美恶清浊之分。而喜怒哀乐未发之时。气不用事。盖此时恶自沉在下面。善之本体。灿然而在中。则尤翁所谓善一边者。非是之谓欤。大率未生已生。便是未发也已发也。方其未生之前。此理至善。则大易继善之谓也。这便是未发气像也。及夫已生之后。性之本体。蔼然呈露于四端之感动。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这便是已发光景也。愚尝以尤翁善一边之说。谓可骇。及到未发之时。恶自沉在下面。善之本体呈露之说。推以究之。则其本体之呈露者。岂非善一边耶。朱子曰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然则善一边之说。未必无所自来矣。程子曰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器亦道道亦器。愚尝答慎晦叔书曰。形而上虽谓之道。而器亦在其中。何以明其然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盖阴阳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6L 页
 器也。而其所以为阴阳者道也。晦叔不以为然。观朱子答吕子约书曰。今且以来示所引一阴一阳。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气像等说。合而析之。则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之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无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不可槩谓形而上者为道之体。天下之达道五。为道之用也。推是观之。则程子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之训。不待明辨而晓然无疑。愚之所答于晦叔者。亦偶有一得矣。
器也。而其所以为阴阳者道也。晦叔不以为然。观朱子答吕子约书曰。今且以来示所引一阴一阳。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漠气像等说。合而析之。则阴阳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万象之纷罗者也。是数者。各有当然之理。即所谓道也。当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无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体。而其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不可槩谓形而上者为道之体。天下之达道五。为道之用也。推是观之。则程子所谓器亦道道亦器之训。不待明辨而晓然无疑。愚之所答于晦叔者。亦偶有一得矣。张子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朱子曰阴阳循环如磨。游气纷扰。如磨中出者。易曰刚柔相磨。八卦相荡。此阴阳之循环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气之纷扰也。由是推之则气之流行。人物所禀。犬与犬不同。牛与牛不同。人与人不同。人得其气之正且通。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此乾男坤女之合而成质而万殊者也。若论本原则朱子所谓即有理然后有气。故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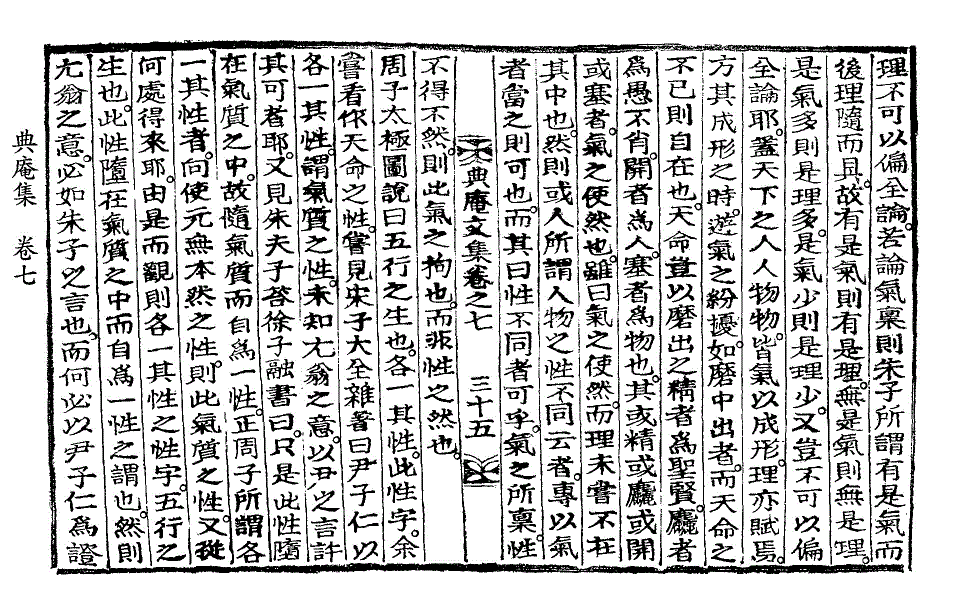 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气禀则朱子所谓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盖天下之人人物物。皆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方其成形之时。游气之纷扰。如磨中出者。而天命之不已则自在也。天命岂以磨出之精者为圣贤。粗者为愚不肖。开者为人。塞者为物也。其或精或粗或开或塞者。气之使然也。虽曰气之使然。而理未尝不在其中也。然则或人所谓人物之性不同云者。专以气者当之则可也。而其曰性不同者可乎。气之所禀。性不得不然。则此气之拘也。而非性之然也。
理不可以偏全论。若论气禀则朱子所谓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又岂不可以偏全论耶。盖天下之人人物物。皆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方其成形之时。游气之纷扰。如磨中出者。而天命之不已则自在也。天命岂以磨出之精者为圣贤。粗者为愚不肖。开者为人。塞者为物也。其或精或粗或开或塞者。气之使然也。虽曰气之使然。而理未尝不在其中也。然则或人所谓人物之性不同云者。专以气者当之则可也。而其曰性不同者可乎。气之所禀。性不得不然。则此气之拘也。而非性之然也。周子太极图说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此性字。余尝看作天命之性。尝见宋子大全杂著曰尹子仁以各一其性。谓气质之性。未知尤翁之意。以尹之言许其可者耶。又见朱夫子答徐子融书曰。只是此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气质而自为一性。正周子所谓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耶。由是而观则各一其性之性字。五行之生也。此性堕在气质之中而自为一性之谓也。然则尤翁之意。必如朱子之言也。而何必以尹子仁为證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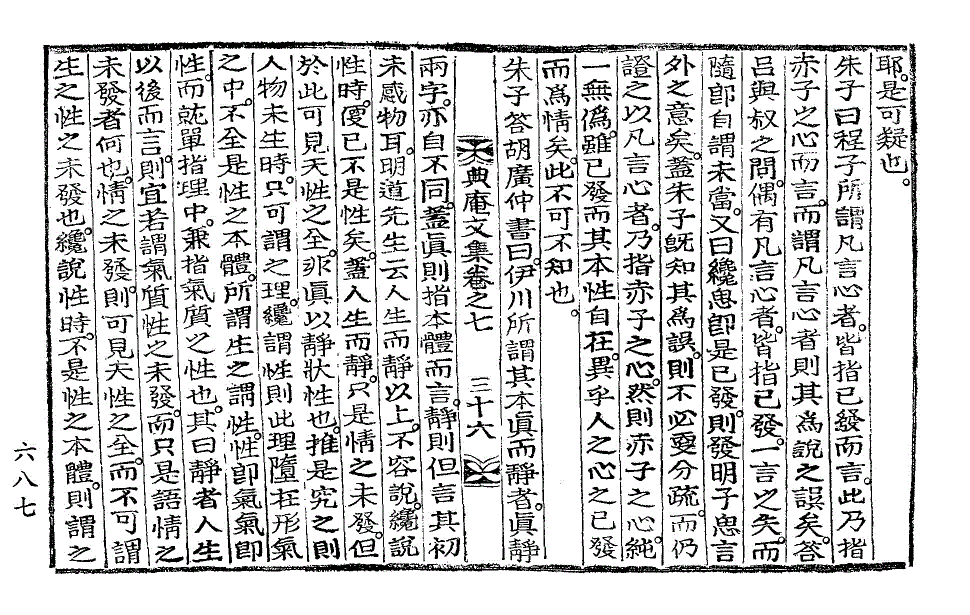 耶。是可疑也。
耶。是可疑也。朱子曰程子所谓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谓凡言心者则其为说之误矣。答吕与叔之问。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发。一言之失。而随即自谓未当。又曰才思即是已发。则发明子思言外之意矣。盖朱子既知其为误。则不必更分疏。而仍證之以凡言心者。乃指赤子之心。然则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虽已发而其本性自在。异乎人之心之已发而为情矣。此不可不知也。
朱子答胡广仲书曰。伊川所谓其本真而静者。真静两字。亦自不同。盖真则指本体而言。静则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矣。盖人生而静。只是情之未发。但于此可见天性之全。非真以静状性也。推是究之则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才谓性则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所谓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而就单指理中。兼指气质之性也。其曰静者人生以后而言。则宜若谓气质性之未发。而只是语情之未发者何也。情之未发。则可见天性之全。而不可谓生之性之未发也。才说性时。不是性之本体。则谓之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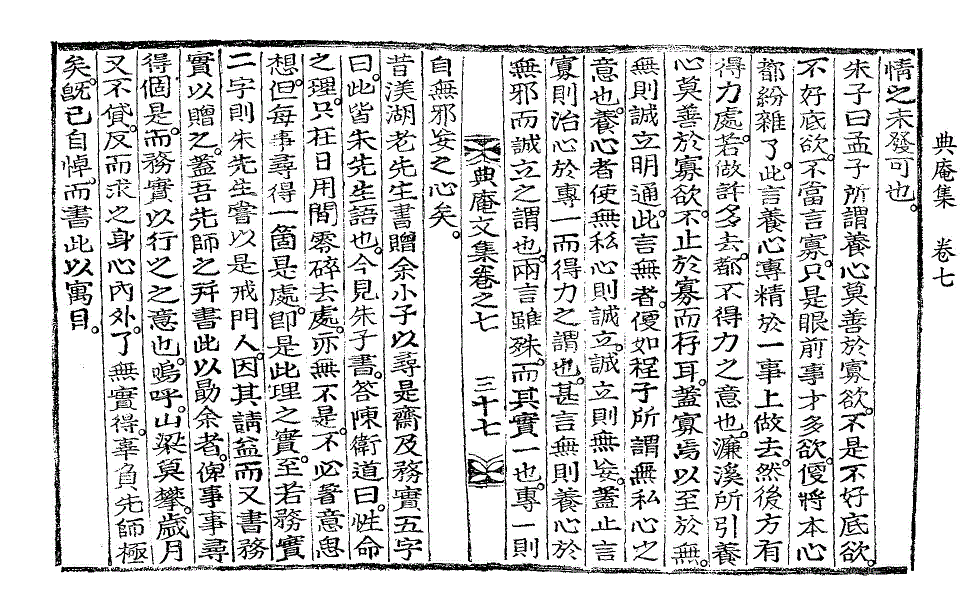 情之未发可也。
情之未发可也。朱子曰孟子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当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将本心都纷杂了。此言养心专精于一事上做去。然后方有得力处。若做许多去。都不得力之意也。濂溪所引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此言无者。便如程子所谓无私心之意也。养心者使无私心则诚立。诚立则无妄。盖止言寡则治心于专一而得力之谓也。甚言无则养心于无邪而诚立之谓也。两言虽殊。而其实一也。专一则自无邪妄之心矣。
昔渼湖老先生书赠余小子以寻是斋及务实五字曰。此皆朱先生语也。今见朱子书。答陈卫道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间零碎去处。亦无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寻得一个是处。即是此理之实。至若务实二字则朱先生尝以是戒门人。因其请益而又书务实以赠之。盖吾先师之并书此以勖余者。俾事事寻得个是。而务实以行之之意也。呜呼。山梁莫攀。岁月又不贷。反而求之身心内外。了无实得。辜负先师极矣。既已自悼。而书此以寓目。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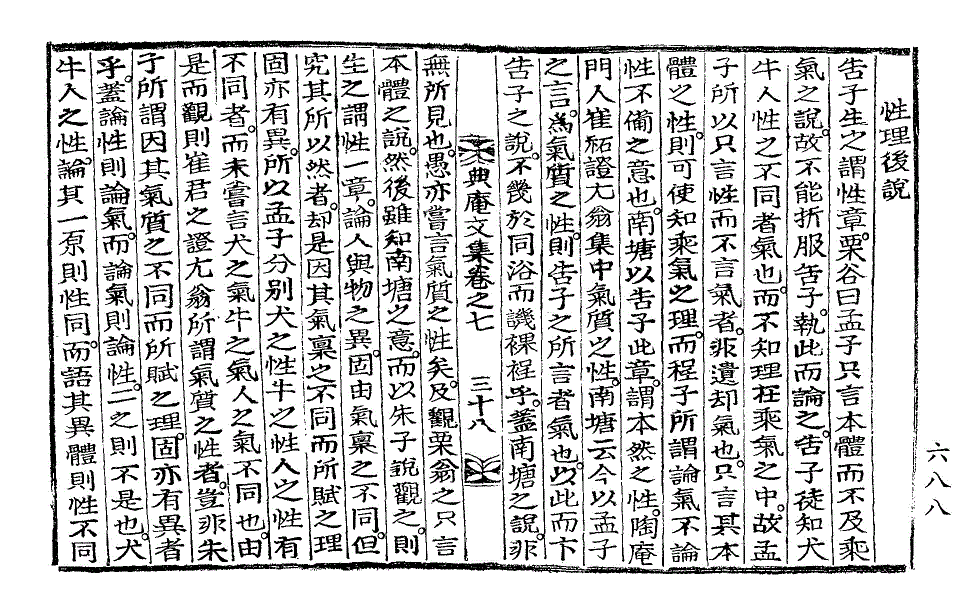 性理后说
性理后说告子生之谓性章。栗谷曰孟子只言本体而不及乘气之说。故不能折服告子。执此而论之。告子徒知犬牛人性之不同者气也。而不知理在乘气之中。故孟子所以只言性而不言气者。非遗却气也。只言其本体之性。则可使知乘气之理。而程子所谓论气不论性不备之意也。南塘以告子此章。谓本然之性。陶庵门人崔祏證尤翁集中气质之性。南塘云今以孟子之言。为气质之性。则告子之所言者气也。以此而卞告子之说。不几于同浴而讥裸裎乎。盖南塘之说。非无所见也。愚亦尝言气质之性矣。及观栗翁之只言本体之说。然后虽知南塘之意。而以朱子说观之。则生之谓性一章。论人与物之异。固由气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气禀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尝言犬之气牛之气人之气不同也。由是而观则崔君之證尤翁所谓气质之性者。岂非朱子所谓因其气质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者乎。盖论性则论气。而论气则论性。二之则不是也。犬牛人之性。论其一原则性同。而语其异体则性不同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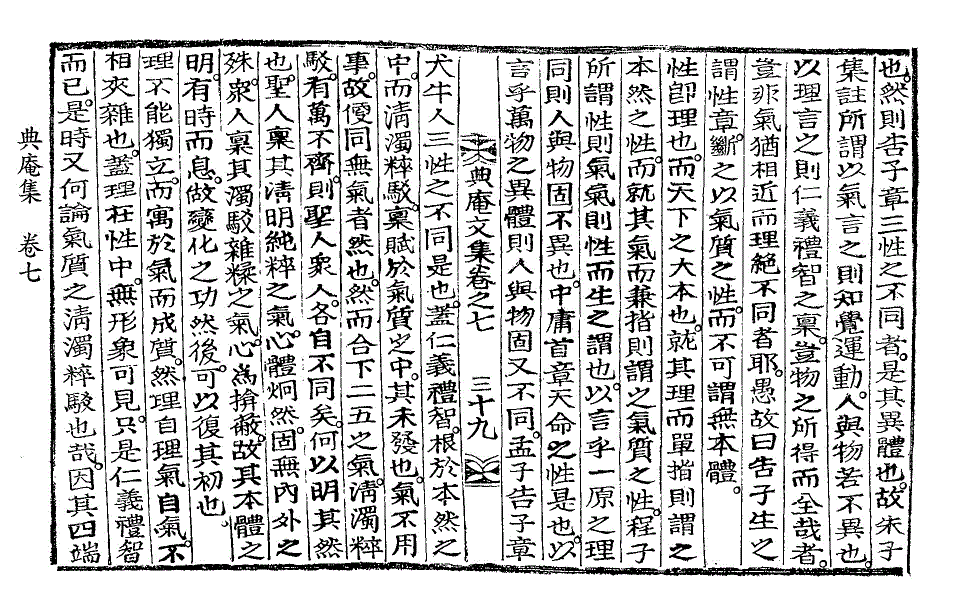 也。然则告子章三性之不同者。是其异体也。故朱子集注所谓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者。岂非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愚故曰告子生之谓性章。断之以气质之性。而不可谓无本体。
也。然则告子章三性之不同者。是其异体也。故朱子集注所谓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者。岂非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愚故曰告子生之谓性章。断之以气质之性。而不可谓无本体。性即理也。而天下之大本也。就其理而单指则谓之本然之性。而就其气而兼指则谓之气质之性。程子所谓性则气气则性而生之谓也。以言乎一原之理同则人与物固不异也。中庸首章天命之性是也。以言乎万物之异体则人与物固又不同。孟子告子章犬牛人三性之不同是也。盖仁义礼智。根于本然之中。而清浊粹驳。禀赋于气质之中。其未发也。气不用事。故便同无气者然也。然而合下二五之气。清浊粹驳。有万不齐。则圣人众人。各自不同矣。何以明其然也。圣人禀其清明纯粹之气。心体炯然。固无内外之殊。众人禀其浊驳杂糅之气。心为掩蔽。故其本体之明。有时而息。做变化之功然后。可以复其初也。
理不能独立。而寓于气而成质。然理自理气自气。不相夹杂也。盖理在性中。无形象可见。只是仁义礼智而已。是时又何论气质之清浊粹驳也哉。因其四端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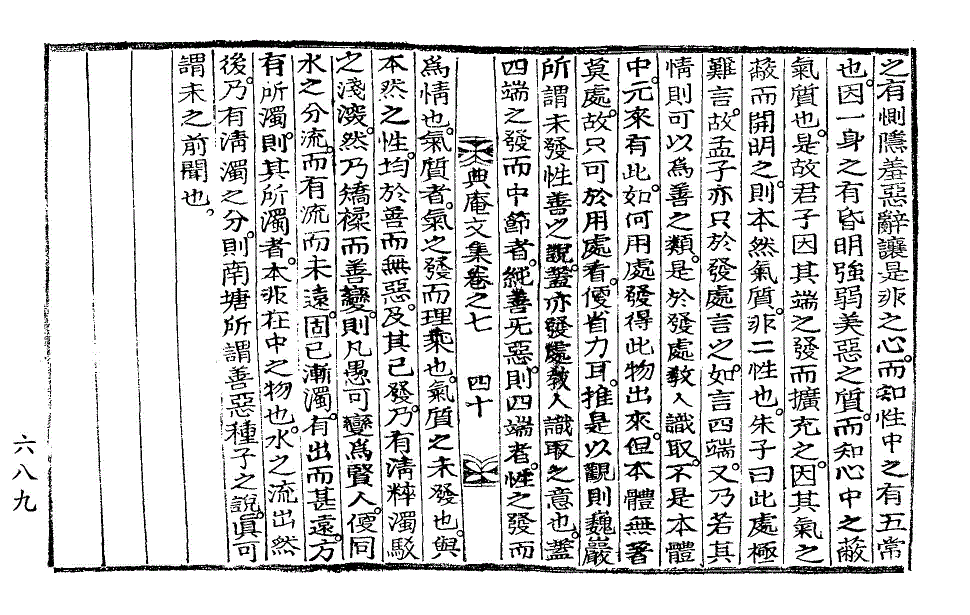 之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知性中之有五常也。因一身之有昏明强弱美恶之质。而知心中之蔽气质也。是故君子因其端之发而扩充之。因其气之蔽而开明之。则本然气质。非二性也。朱子曰此处极难言。故孟子亦只于发处言之。如言四端。又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类。是于发处教人识取。不是本体中。元来有此。如何用处发得此物出来。但本体无著莫处。故只可于用处看。便省力耳。推是以观则巍岩所谓未发性善之说。盖亦发处教人识取之意也。盖四端之发而中节者。纯善无恶。则四端者。性之发而为情也。气质者。气之发而理乘也。气质之未发也。与本然之性。均于善而无恶。及其已发。乃有清粹浊驳之浅深。然乃矫楺而善变。则凡愚可变为贤人。便同水之分流。而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则其所浊者。本非在中之物也。水之流出然后。乃有清浊之分。则南塘所谓善恶种子之说。真可谓未之前闻也。
之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知性中之有五常也。因一身之有昏明强弱美恶之质。而知心中之蔽气质也。是故君子因其端之发而扩充之。因其气之蔽而开明之。则本然气质。非二性也。朱子曰此处极难言。故孟子亦只于发处言之。如言四端。又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类。是于发处教人识取。不是本体中。元来有此。如何用处发得此物出来。但本体无著莫处。故只可于用处看。便省力耳。推是以观则巍岩所谓未发性善之说。盖亦发处教人识取之意也。盖四端之发而中节者。纯善无恶。则四端者。性之发而为情也。气质者。气之发而理乘也。气质之未发也。与本然之性。均于善而无恶。及其已发。乃有清粹浊驳之浅深。然乃矫楺而善变。则凡愚可变为贤人。便同水之分流。而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则其所浊者。本非在中之物也。水之流出然后。乃有清浊之分。则南塘所谓善恶种子之说。真可谓未之前闻也。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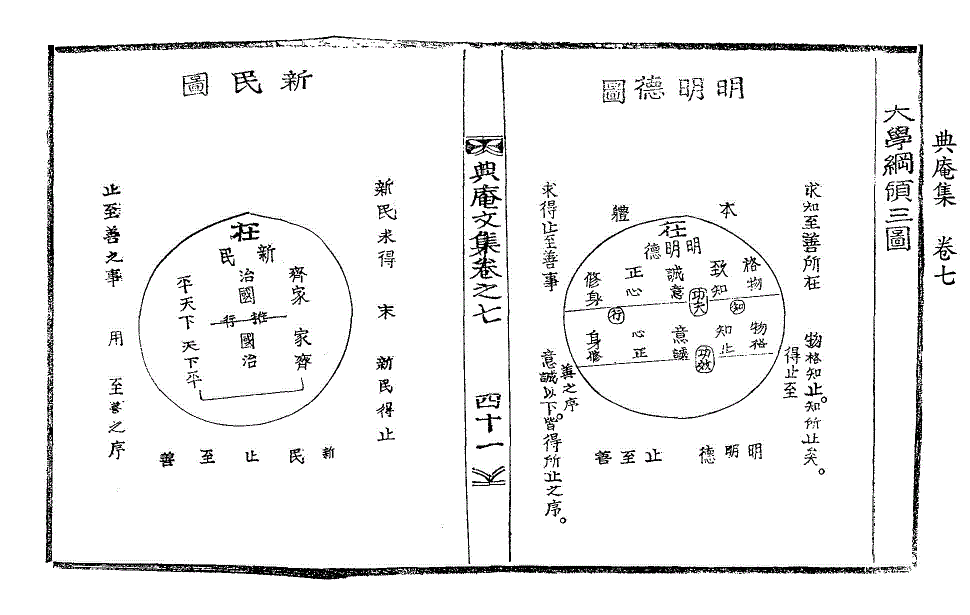 大学纲领三图
大学纲领三图明明德图
삽화 새창열기
新民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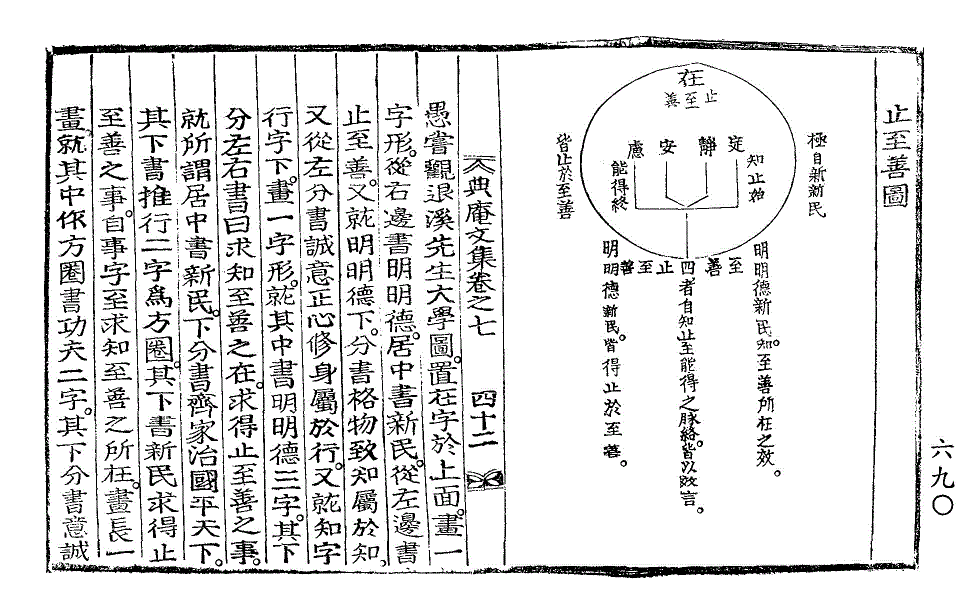 止至善图
止至善图삽화 새창열기
愚尝观退溪先生大学图。置在字于上面。画一字形。从右边书明明德。居中书新民。从左边书止至善。又就明明德下。分书格物致知属于知。又从左分书诚意正心修身属于行。又就知字行字下。画一字形。就其中书明明德三字。其下分左右书曰求知至善之在。求得止至善之事。就所谓居中书新民。下分书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下书推行二字为方圈。其下书新民求得止至善之事。自事字至求知至善之所在。画长一画。就其中作方圈书功夫二字。其下分书意诚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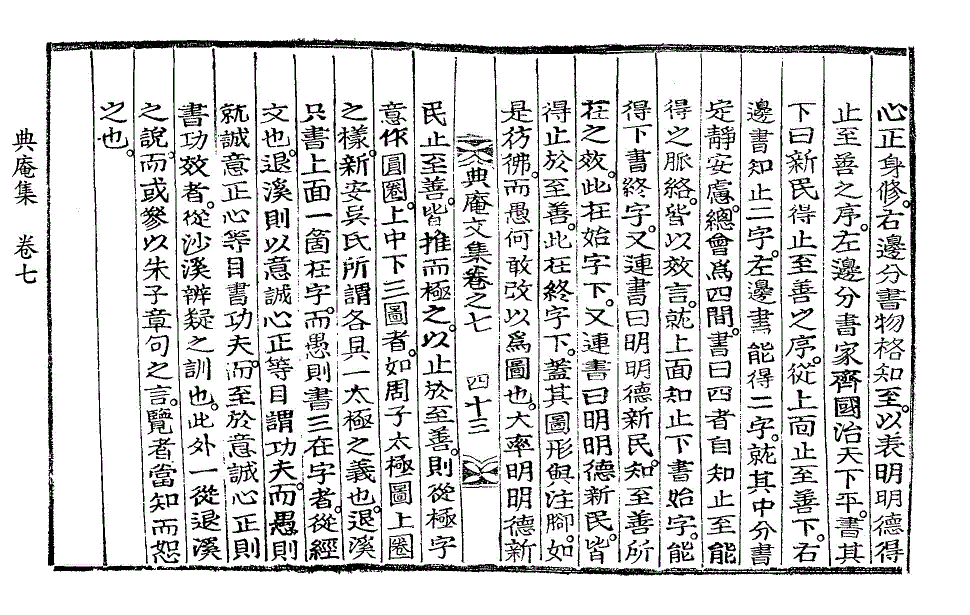 心正身修。右边分书物格知至。以表明明德得止至善之序。左边分书家齐国治天下平。书其下曰新民得止至善之序。从上面止至善下。右边书知止二字。左边书能得二字。就其中分书定静安虑。总会为四间。书曰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脉络。皆以效言。就上面知止下书始字。能得下书终字。又连书曰明明德新民。知至善所在之效。此在始字下。又连书曰明明德新民。皆得止于至善。此在终字下。盖其图形与注脚。如是彷佛。而愚何敢改以为图也。大率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推而极之。以止于至善。则从极字意作圆圈。上中下三图者。如周子太极图上圈之样。新安吴氏所谓各具一太极之义也。退溪只书上面一个在字。而愚则书三在字者。从经文也。退溪则以意诚心正等目谓功夫。而愚则就诚意正心等目书功夫。而至于意诚心正则书功效者。从沙溪辨疑之训也。此外一从退溪之说。而或参以朱子章句之言。览者当知而恕之也。
心正身修。右边分书物格知至。以表明明德得止至善之序。左边分书家齐国治天下平。书其下曰新民得止至善之序。从上面止至善下。右边书知止二字。左边书能得二字。就其中分书定静安虑。总会为四间。书曰四者自知止至能得之脉络。皆以效言。就上面知止下书始字。能得下书终字。又连书曰明明德新民。知至善所在之效。此在始字下。又连书曰明明德新民。皆得止于至善。此在终字下。盖其图形与注脚。如是彷佛。而愚何敢改以为图也。大率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推而极之。以止于至善。则从极字意作圆圈。上中下三图者。如周子太极图上圈之样。新安吴氏所谓各具一太极之义也。退溪只书上面一个在字。而愚则书三在字者。从经文也。退溪则以意诚心正等目谓功夫。而愚则就诚意正心等目书功夫。而至于意诚心正则书功效者。从沙溪辨疑之训也。此外一从退溪之说。而或参以朱子章句之言。览者当知而恕之也。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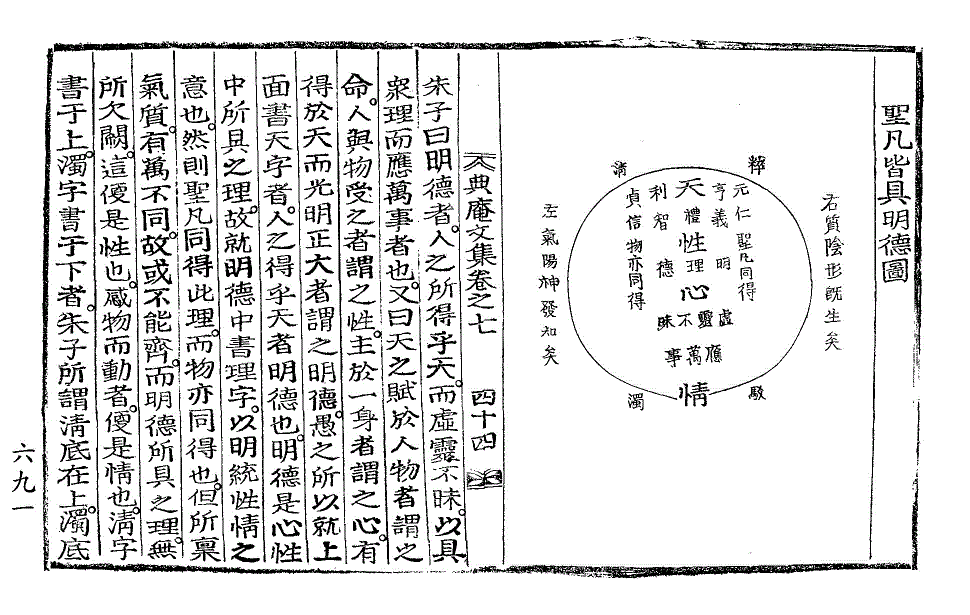 圣凡皆具明德图
圣凡皆具明德图삽화 새창열기
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又曰天之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愚之所以就上面书天字者。人之得乎天者明德也。明德是心性中所具之理。故就明德中书理字。以明统性情之意也。然则圣凡同得此理。而物亦同得也。但所禀气质。有万不同。故或不能齐。而明德所具之理。无所欠阙。这便是性也。感物而动者。便是情也。清字书于上。浊字书于下者。朱子所谓清底在上。浊底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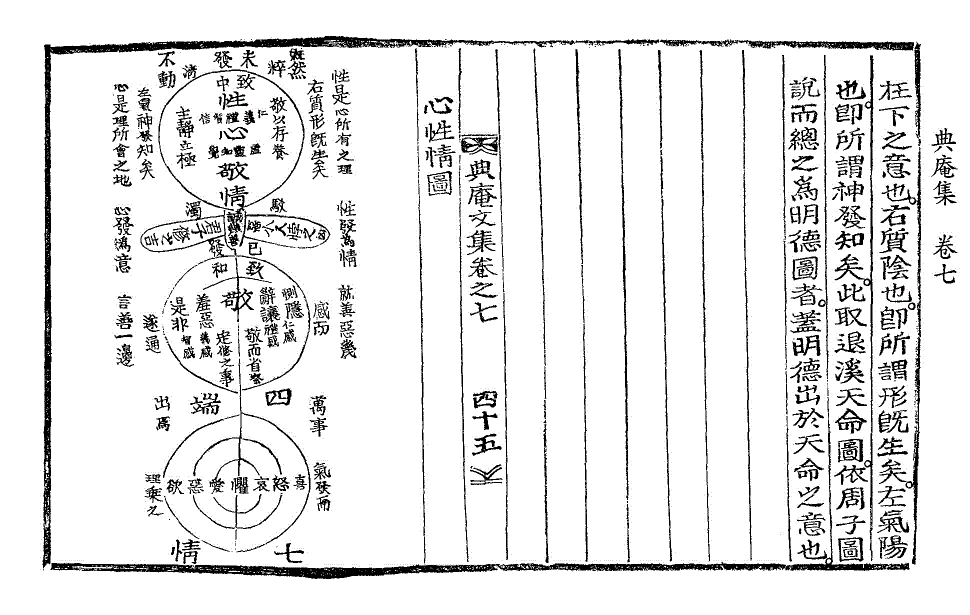 在下之意也。右质阴也。即所谓形既生矣。左气阳也。即所谓神发知矣。此取退溪天命图。依周子图说而总之为明德图者。盖明德出于天命之意也。
在下之意也。右质阴也。即所谓形既生矣。左气阳也。即所谓神发知矣。此取退溪天命图。依周子图说而总之为明德图者。盖明德出于天命之意也。心性情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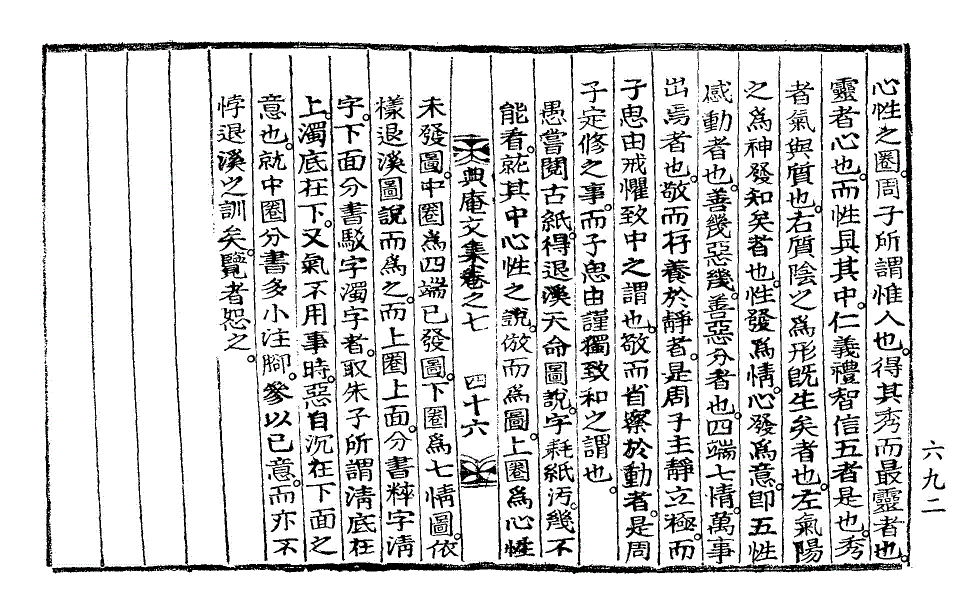 心性之圈。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形既生矣者也。左气阳之为神发知矣者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五性感动者也。善几恶几。善恶分者也。四端七情。万事出焉者也。敬而存养于静者。是周子主静立极。而子思由戒惧致中之谓也。敬而省察于动者。是周子定修之事。而子思由谨独致和之谓也。
心性之圈。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形既生矣者也。左气阳之为神发知矣者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五性感动者也。善几恶几。善恶分者也。四端七情。万事出焉者也。敬而存养于静者。是周子主静立极。而子思由戒惧致中之谓也。敬而省察于动者。是周子定修之事。而子思由谨独致和之谓也。愚尝阅古纸。得退溪天命图说。字耗纸污。几不能看。就其中心性之说。仿而为图。上圈为心性未发图。中圈为四端已发图。下圈为七情图。依样退溪图说而为之。而上圈上面。分书粹字清字。下面分书驳字浊字者。取朱子所谓清底在上。浊底在下。又气不用事时。恶自沉在下面之意也。就中圈分书多小注脚。参以己意。而亦不悖退溪之训矣。览者恕之。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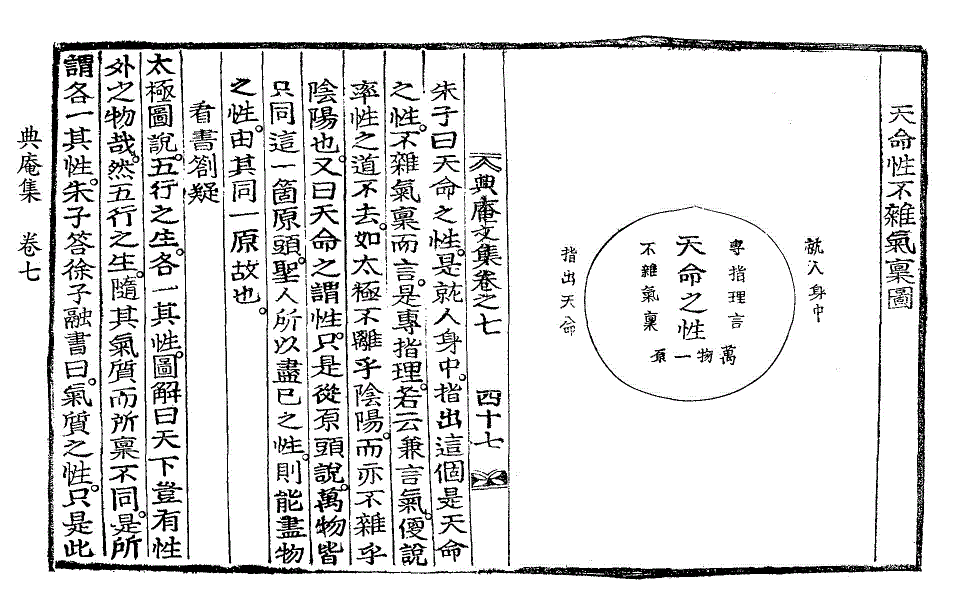 天命性不杂气禀图
天命性不杂气禀图삽화 새창열기
朱子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是专指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极不离乎阴阳。而亦不杂乎阴阳也。又曰天命之谓性。只是从原头说。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
看书劄疑
太极图说。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图解曰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是所谓各一其性。朱子答徐子融书曰。气质之性。只是此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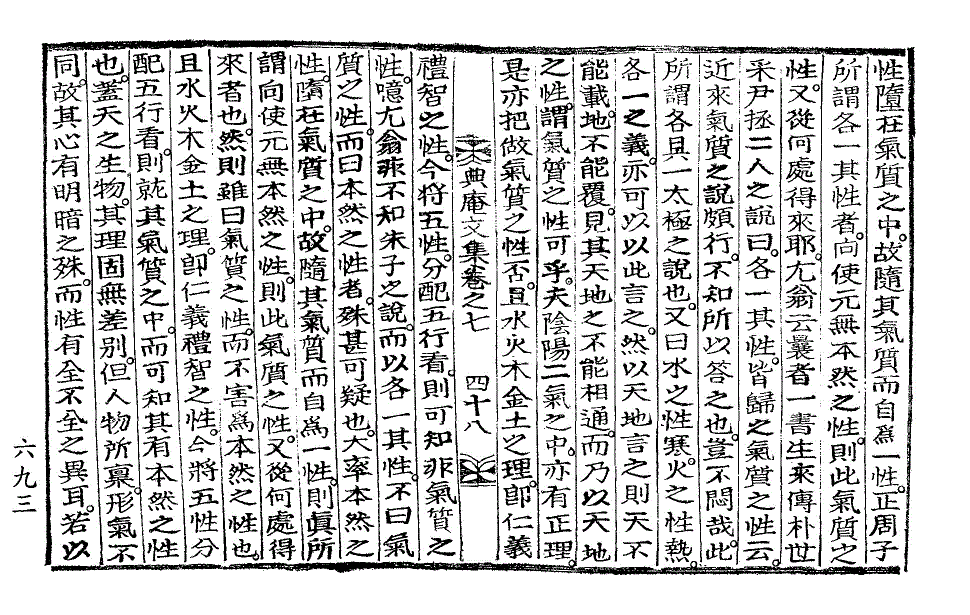 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其气质而自为一性。正周子所谓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耶。尤翁云曩者一书生来传朴世采尹拯二人之说曰。各一其性。皆归之气质之性云。近来气质之说颇行。不知所以答之也。岂不闷哉。此所谓各具一太极之说也。又曰水之性寒。火之性热。各一之义。亦可以以此言之。然以天地言之则天不能载。地不能覆。见其天地之不能相通。而乃以天地之性。谓气质之性可乎。夫阴阳二气之中。亦有正理。是亦把做气质之性否。且水火木金土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今将五性。分配五行看。则可知非气质之性。噫尤翁非不知朱子之说。而以各一其性。不曰气质之性。而曰本然之性者。殊甚可疑也。大率本然之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其气质而自为一性。则真所谓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者也。然则虽曰气质之性。而不害为本然之性也。且水火木金土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今将五性分配五行看。则就其气质之中。而可知其有本然之性也。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耳。若以
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其气质而自为一性。正周子所谓各一其性者。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耶。尤翁云曩者一书生来传朴世采尹拯二人之说曰。各一其性。皆归之气质之性云。近来气质之说颇行。不知所以答之也。岂不闷哉。此所谓各具一太极之说也。又曰水之性寒。火之性热。各一之义。亦可以以此言之。然以天地言之则天不能载。地不能覆。见其天地之不能相通。而乃以天地之性。谓气质之性可乎。夫阴阳二气之中。亦有正理。是亦把做气质之性否。且水火木金土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今将五性。分配五行看。则可知非气质之性。噫尤翁非不知朱子之说。而以各一其性。不曰气质之性。而曰本然之性者。殊甚可疑也。大率本然之性。堕在气质之中。故随其气质而自为一性。则真所谓向使元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又从何处得来者也。然则虽曰气质之性。而不害为本然之性也。且水火木金土之理。即仁义礼智之性。今将五性分配五行看。则就其气质之中。而可知其有本然之性也。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耳。若以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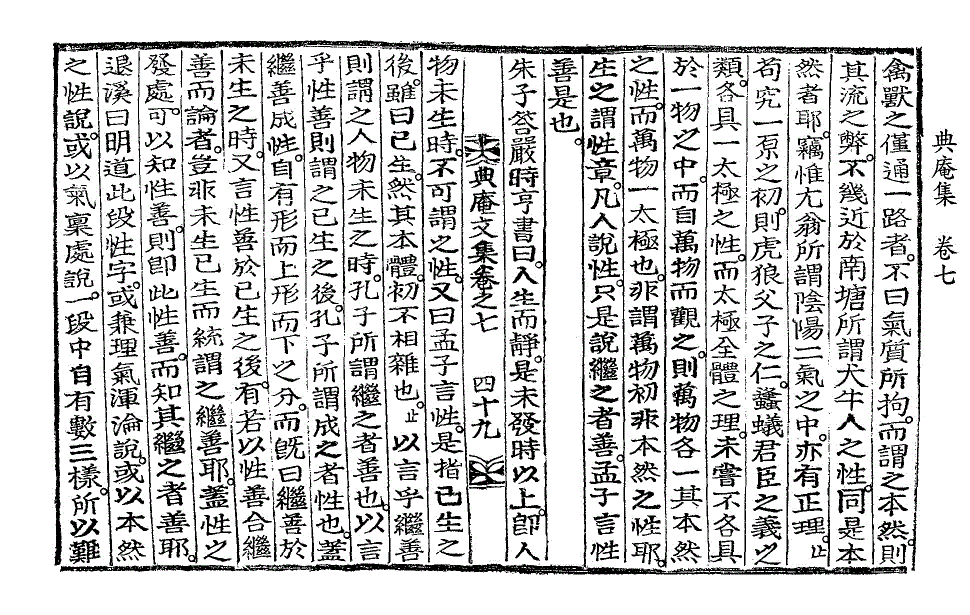 禽兽之仅通一路者。不曰气质所拘。而谓之本然。则其流之弊。不几近于南塘所谓犬牛人之性。同是本然者耶。窃惟尤翁所谓阴阳二气之中。亦有正理。(止。)苟究一原之初。则虎狼父子之仁。蜂蚁君臣之义之类。各具一太极之性。而太极全体之理。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本然之性。而万物一太极也。非谓万物初非本然之性耶。生之谓性章。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
禽兽之仅通一路者。不曰气质所拘。而谓之本然。则其流之弊。不几近于南塘所谓犬牛人之性。同是本然者耶。窃惟尤翁所谓阴阳二气之中。亦有正理。(止。)苟究一原之初。则虎狼父子之仁。蜂蚁君臣之义之类。各具一太极之性。而太极全体之理。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本然之性。而万物一太极也。非谓万物初非本然之性耶。生之谓性章。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人物未生时。不可谓之性。又曰孟子言性。是指已生之后。虽曰已生。然其本体。初不相杂也。(止。)以言乎继善则谓之人物未生之时。孔子所谓继之者善也。以言乎性善则谓之已生之后。孔子所谓成之者性也。盖继善成性。自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而既曰继善于未生之时。又言性善于已生之后。有若以性善合继善而论者。岂非未生已生而统谓之继善耶。盖性之发处。可以知性善。则即此性善。而知其继之者善耶。退溪曰明道此段性字。或兼理气浑沦说。或以本然之性说。或以气禀处说。一段中自有数三样。所以难
典庵文集卷之七 第 6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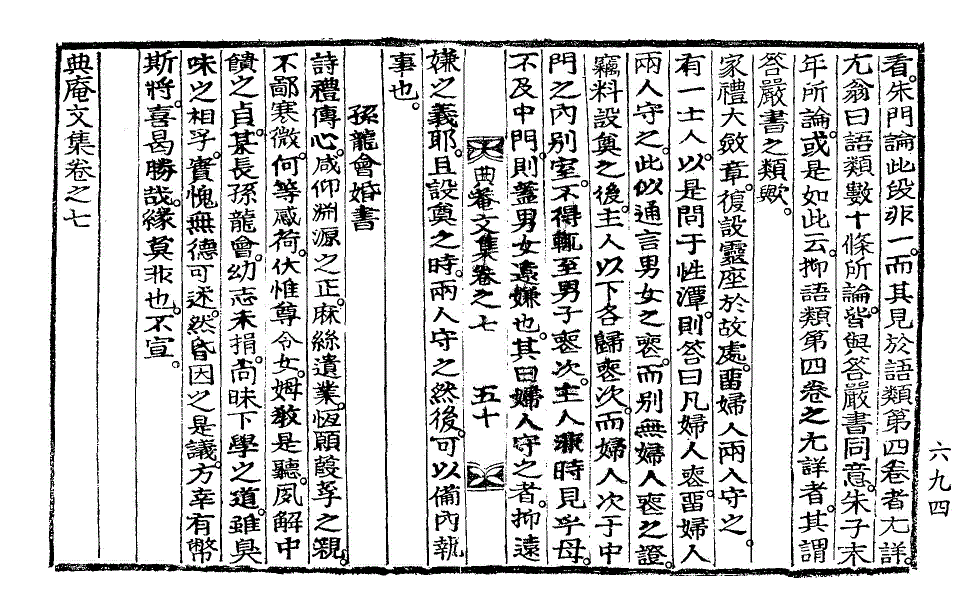 看。朱门论此段非一。而其见于语类第四卷者尤详。尤翁曰语类数十条所论。皆与答严书同意。朱子末年所论。或是如此云。抑语类第四卷之尤详者。其谓答严书之类欤。
看。朱门论此段非一。而其见于语类第四卷者尤详。尤翁曰语类数十条所论。皆与答严书同意。朱子末年所论。或是如此云。抑语类第四卷之尤详者。其谓答严书之类欤。家礼大敛章。复设灵座于故处。留妇人两人守之。
有一士人。以是问于性潭。则答曰凡妇人丧。留妇人两人守之。此似通言男女之丧。而别无妇人丧之證。窃料设奠之后。主人以下各归丧次。而妇人次于中门之内别室。不得辄至男子丧次。主人非时见乎母。不及中门。则盖男女远嫌也。其曰妇人守之者。抑远嫌之义耶。且设奠之时。两人守之然后。可以备内执事也。
孙龙会婚书
诗礼传心。咸仰渊源之正。麻丝遗业。恒愿葭莩之亲。不鄙寒微。何等感荷。伏惟尊令女。姆教是听。夙解中馈之贞。某长孙龙会。幼志未捐。尚昧下学之道。虽臭味之相孚。实愧无德可述。然昏因之是议。方幸有币斯将。喜曷胜哉。缘莫非也。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