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典庵文集卷之四
书
书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2H 页
 上渼湖先生
上渼湖先生拜违函席。忽已数月。归途付一书于槐山递。窃计已获关听也。未审先生道体若何。閤患近有勿药之喜耶。小子归路入延丰双溪洞中。山行百馀里。往往有川声岳色之可娱者。又三十里许。有所谓曦阳峰白云台。其山川之灵怪。岩石之绝奇。虽俗离之云壮。华阳之巴谷。恐无以过此。恨未陪杖屦于其间。与闻仁智之妙也。八月十日还乡。老人气力粗安。身又无扰。私幸何达。向蒙劄着之教。日夕戒惧。欲寡其过。而较前叨诲之日。如未百倍其功。将不免卤莽一庸人。每中夜思之。背汗而沾衣也。方继读鲁论。而间有疑义之难解处。此其粗疏不精细之病根尚在而然也。屏居静室。思索有未究者。即记小册子。将欲更质于他日请益之时。而未知其间能无前却而专一否耶。人物性同异之说。讲之已熟。不必更告。而敢以或说问答。别纸以呈。此未免高谈每及性命之病也。李明叟久侍门屏。其课读想已了当。今冬有相聚牙山之约。得以讲讨绪论。何幸如之。未间更乞为道保重。以慰瞻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2L 页
 仰。
仰。上渼湖先生
辞退行窝。岁色垂暮。而穷居乏人。一未得探候。此岂弟子之职哉。愧悚之极。不知所以置躬也。中间仍黄溪去人。附上一书。而此是转便。安保其必获关听也。伏不审调体候摄理之久。果无损而有效。且群居问难。无甚其酬应之劳否。夏间因郑生就毅书。始闻门下疟渐之报。月前得李明叟书。审有令孙妇之丧。伏虑之馀。又不胜惊愕也。伏惟慈爱隆深。悲恸何堪。伏乞循理宽抑。为道保重。则斯文之幸。当如何哉。南尚宽之诬录问答。亦一世变也。且其徒党之往来于湖岭者。胥动浮言。猖狂自恣。宁欲洗耳而不闻也。然门下盛德粹言。无一可摘疵指瑕。则彼不过妄人而已。又何足动吾一发哉。门生春夏以来。亲忧儿病。种种相仍。至于读书收敛之功。未能专一。而秋冬以后。稍似开霁。仍其隙也。携书入山。温理旧业。而见无朋友之益。其固陋离索之叹。何可尽喻。中庸二十二章以下。前春就讲之时。未及卒业。今又继读。而疑难者甚多。敢此别录以上。幸一一批诲。则谨当受焉服膺耳。俟明春更欲洒扫于行轩之下。未知其间或无还次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3H 页
 于渼江否。青山韩生想恒侍。而其馀诸生来学者。未知有几也。自顾无状。地远家穷。一曝未易。寻常愧汗而沾衣也。周童子元稷依教授句读。而其向学之诚尤可尚。
于渼江否。青山韩生想恒侍。而其馀诸生来学者。未知有几也。自顾无状。地远家穷。一曝未易。寻常愧汗而沾衣也。周童子元稷依教授句读。而其向学之诚尤可尚。上渼湖先生
半月中庸之诲。恍然受得其要领。而归日匆匆。未卒其业。则从师讲说。亦有命存焉耶。拜违函席。忽已一旬。气候不审若何。小子中路遇雨雪首尾五日。间关还第。老人气力而免甚损。而日前遭堂叔母丧。其他疾病相仍。悲苦交深。难以尽达。受读之书。归而更绎。庶不忘其旧闻。而自致曲章以下。虽未及详质。然既闻其次第纲领。则恁地读了。以俟他日请益。可以逐条仰质耳。沂上讲会。寒川诸益。谋聚于八月望后。此时如讲中庸。则小子之未尽闻于函丈者。从可与论于朋友间耶。华阳事。先生向来处义。恐亦稳当。而明叟之意。亦以当出为言。则小子之愚不敢知也。今夏又或经过于稽山否。此去稍近。政好就正。而为先生计。不如归卧渼江。以践白鸥旧盟。且云楼三席。复修前讲。则小子虽无似。从此负笈。
上渼湖先生疑礼问目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3L 页
 问祭考妣。并设一卓。而饭羹饼面则随位各设。其他庶品。合设兼享。不其未安耶。
问祭考妣。并设一卓。而饭羹饼面则随位各设。其他庶品。合设兼享。不其未安耶。答。死者精神之合也。并设亦礼也。
前后妣神位。共安其考椟中。得无未安乎。
父之妻。岂有前后之别也。皆合椟可矣。备要有朱子正论。
夫祭妻。有故不参。则使子行之。而读祝时无人代读。则其子之读父名。甚未安奈何。
父命之则子何敢不读也。吾家先祖祭时。使儿子读吾名矣。当祭者虽有祭祖祭妻之别。而其为子读父名。而有未安之心则一般。然其于父命何哉。
祭时进茶抄饭否。
此丧中葬前之礼。葬后则阙之。
心丧中遭期服。则当服何服。
当服期服。
祭时出主。抑有轻重否。
礼云出主于座。座者椟也。但望日不出主。而朔日则出主。盖望日轻而朔日稍重之义也。然则祭无小大。皆可出主也。(若俗节在望日。则设酒出主。)
祖考祭时。诸孙之哭与不哭。有据否。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4H 页
 孙于祖考妣。不得逮事。则不哭常道也。然自然有哀痛之心则何可不哭也。不然而随诸父而强哭。则祖孙之间。无诚实者也。不如不哭之为愈。朱子曰逮事于祖考妣则可哭。而不逮事则不当哭。
孙于祖考妣。不得逮事。则不哭常道也。然自然有哀痛之心则何可不哭也。不然而随诸父而强哭。则祖孙之间。无诚实者也。不如不哭之为愈。朱子曰逮事于祖考妣则可哭。而不逮事则不当哭。往吊人家。无泪强哭。不可乎。
凡无真情而强哭者。非天理也。
吊时或立哭或伏哭。何者为是。
伏哭是。
葬时。丧人以下皆临圹而哭拜何如。
临圹而拜。长子赠玄纁时。礼也。次子则不拜。
时祭不惟宗家行之。只祭考妣者。亦可行之否。宗家若徇俗不行此祭。则支子独行此祭。得无未安于宗家否。
时祭岂惟宗家而止哉。只祭考妣者。亦可行之。宗家若贫不能行。支庶助祭需好矣。而若难助需则虽独行亦何妨耶。以生人推之则亦一理也。宗家若贫不能养其亲。则支孙家亦从而不养其亲乎。
祭时无他执事。而只与夫妇同祭。则献酌时。主人自斟酒献于位。主妇自斟酒献于位。而无夫妇授受之义否。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4L 页
 似然。
似然。祭品一从家礼定式否。家力有馀则虽过于定式。亦无害否。
当以家礼为定规。而或临时得其好味。虽过于定数。合于情而无害于礼。或临时不得祭品。虽违于定数。出于势而亦无害于礼。大率家礼祭品。虽似𥳑略。而通上下之礼也。有馀之家。虽若薄约。而以贫家而观则于此定规。亦难一一办备。盖人家有馀之时。或盛备祭品。过于定规。而至于子孙艰穷之时。不忍违古薄设。仍以阙祭。此终不若以家礼祭品。为一定之规也。昔重峰告于其继母曰某日将行时祭。敢以为请。母曰吾家素贫。不行此祭久矣。汝何以办行耶。重峰曰母若许可则办行非所虑也。母曰诺。乃退而省其私。获黍于山。剪菜于园。卒以行祀。其母笑曰尔之祭。其不难矣。慎独斋当光海朝。僻处乡里。只得石鱼数头。而仍为祭需。同春之祭也。或得时物可用者。则其品虽过于家礼而亦用之。尤翁之祭也。或值潦水。无以办需。则虽不及于家礼。而不为苟且得用。是故吾尝曰祭品务以精洁可也。与其欠诚洁而贵礼侈。不若欠丰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5H 页
 侈而贵诚洁也。
侈而贵诚洁也。时祭之比忌祭。轻重何如。
时祭之义重矣。古人皆以时祭为祭。祭名之所以出也。呜呼。时祭之不行者有之矣。是故今人家皆知忌祀墓祀之不可不行。而不知时祭之必可行也。以祭之轻重言之。宁阙忌祀。而时祭不可阙也。今人之不行时祭。而只行忌祀者。于此亦可见为己为人之分也。或有忌祀之阙者。则人皆非之。己亦耻之。或有时祭之阙者。则人不以为咎。己亦不耻之。无他。时祭之废。多有矣。仍以成俗。不知其非故也。
祭品图式。从击蒙要诀否。备要与家礼有异。从何参用。
当以丧礼备要为正。
阖门后。立耶伏耶。
当立。
祖父母伯叔父母之丧。期大功以下。或去冠去网巾。未知如何。
家礼有皆去华饰之文。而无去冠之文。今人成服后。咸著吉冠。则似无成服前去冠之理。网巾则决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5L 页
 不可去也。礼虽丧人只有去冠之文。而无去縰之文。縰者今之网巾之类也。后来有被发之俗。故虽去縰。然亦非古礼也。尤庵集有不去冠。恐骇俗之语。则虽从俗去冠可也。不去冠亦可也。
不可去也。礼虽丧人只有去冠之文。而无去縰之文。縰者今之网巾之类也。后来有被发之俗。故虽去縰。然亦非古礼也。尤庵集有不去冠。恐骇俗之语。则虽从俗去冠可也。不去冠亦可也。与徐元礼(有防)
春中仍稽山递。获拜惠书。披慰至今。未有去便。阙然无报。若始未相识者。虽蒙雅恕。而愧悚则深矣。第以教导群蒙。日有成就之乐。闻极深喜。大率此职。虽卑亦重矣。如非其本原之素所蓄积者。不能著其启发之效。而顾足下天姿卓越。学力精笃。固有可为人师者。然足下又以此时。益读平日未读之书。益穷天下未尽之理。而须臾之顷。纤介之微。念念相承。无敢有所间断焉。则庶无自欺欺人之患矣。不亦幸乎。见今吾师之门出而为人师者足下也。挽古救俗。优可以自新新人者。亦足下也。由是以观则先生虽隐德不出。而其馀教之及于人如此。不可谓无补于明时也。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与徐元礼
春中稽山之会。李明叟带高轩安信而来。相对亹亹。慰若书面。未几南下。不获言笑。已踰屡月。真所谓北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6H 页
 望陨涕。有儿女之感也。比来亢暵。伏惟仕履有胜。诱蒙稍乐耶。远不任驰溯之至。鼎焕春夏以来。亲癠儿忧。靡遑读书。而又无彊辅益友可与相责。因循颓惰。虽今日无挠。而一向放豚。收召不至。每中夜以思。不觉肤汗沾衣也。想贤者闻之。不瑕深诛而痛斥耶。丈席近已还山否。坐在远外。久未闻师友安否。自叹离索之甚耳。牌拂密迩。宜于吾兄种种致问。如有斯文之可闻者。一一致及也。向从湖中。得亲金君和仲。其人与诗皆可爱。谓尝托契于兄。故其相赠。累累及元礼交道。思元礼而既不可得。则见元礼之所与交。如见我元礼尔。有相斋记冀兄一览。而随病痛加斤正。因南原官递传致和仲。此其宿诺也。勿泛如何。伯氏尚留治所否。夏窠想好题目。而挠未别幅。早晚相见。幸致此意。
望陨涕。有儿女之感也。比来亢暵。伏惟仕履有胜。诱蒙稍乐耶。远不任驰溯之至。鼎焕春夏以来。亲癠儿忧。靡遑读书。而又无彊辅益友可与相责。因循颓惰。虽今日无挠。而一向放豚。收召不至。每中夜以思。不觉肤汗沾衣也。想贤者闻之。不瑕深诛而痛斥耶。丈席近已还山否。坐在远外。久未闻师友安否。自叹离索之甚耳。牌拂密迩。宜于吾兄种种致问。如有斯文之可闻者。一一致及也。向从湖中。得亲金君和仲。其人与诗皆可爱。谓尝托契于兄。故其相赠。累累及元礼交道。思元礼而既不可得。则见元礼之所与交。如见我元礼尔。有相斋记冀兄一览。而随病痛加斤正。因南原官递传致和仲。此其宿诺也。勿泛如何。伯氏尚留治所否。夏窠想好题目。而挠未别幅。早晚相见。幸致此意。与徐元礼
新使君谓余不鄙。屡过穷庐。语及足下。未尝不怀仰高风也。仍其官递。谨修一书。而尚未蒙赐答。抑中路沉滞。未及关听欤。恒中夜相思。继之以叹曰曩从足下游。窃揣庠生与书生。若无异同。相守而讨论之。相别而书问之。庶没身友善而不衰也。足下被选以来。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6L 页
 出处殊涂。彼此无所窥伺其声光。至于书牍一路。有往而无复。世道交情。一何至此。无已则只可将足下上舍时书翰。付诸座右。与之朝暮遇足矣。何必屡费辞说。独自惓恋也哉。舍伯匆匆赴科。不忍有便无问。要付一字。以候起居。
出处殊涂。彼此无所窥伺其声光。至于书牍一路。有往而无复。世道交情。一何至此。无已则只可将足下上舍时书翰。付诸座右。与之朝暮遇足矣。何必屡费辞说。独自惓恋也哉。舍伯匆匆赴科。不忍有便无问。要付一字。以候起居。答徐元礼
权友还。获承复书。迄未释手。又拜耑札。既感且荷。不知所以为喻。洛下同门。不甚相疏。而一散之后。便若始不相识者多矣。不较此书之有无。随递而辄问。于吾兄独见之也。非平日相知之深。何以及此。尤可感也。先生襄礼。果可利行于九月十四否。未知会者诔者几何人也。自顾无状。日事汤忧。未得进哭于加麻执绋之列。其为终天之恨。没齿而何可忘也。推此而益觉吾兄之云梯绊身。亦尔同情也。未谙其间宥还京第。以伸永诀于即远之日耶。远未闻知。是可吁郁。来喻七月以后。尤有自若等语。不觉泪陨而肠坠。此可以慰先生不亡之灵。而警吾辈已放之心也。大率吾党诸人。各处异乡。虽未得种种对讨。而自有不期之会。相观之益。冀万一有补于先生在世之日矣。今焉已矣。向之所以文会于渼上者。又何处复见耶。譬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7H 页
 如大海无源。百川之鱼。溯流上下。未及达于海。忽然波涸而喁喁如也。何幸吾兄际此登龙。其将波及于西江之一斗耶。今时之责。有甚于涸鳞。望兄思所以变化之如何。
如大海无源。百川之鱼。溯流上下。未及达于海。忽然波涸而喁喁如也。何幸吾兄际此登龙。其将波及于西江之一斗耶。今时之责。有甚于涸鳞。望兄思所以变化之如何。与金三山(履安)
向因李明叟。知有令侄妇之戚。为之惊愕不已。凡丧变之来。虽在家面诀。犹不自堪。况千里承讣。其为悲恸。尤何可胜任耶。伏想先生自闻此报。寝食起居。必有所损。是可远虑。际此至寒。服履何如。忧想区区。罔知攸喻。鼎焕奉亲粗遣。而自度身心不有昏昧。则亦多走作。其无分寸之进可想尔。南尚宽凶书之发。又甚于宋魋之变。诚可寒心也。惟幸执事政清治著。风声动人。虽好齮龁如彼者。未敢容其啄。则此古人云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执事之由小县得大州。从可以想也。虽然为执事得大州。非谓许多州牧。而莅吾南土。至比使此固陋。得以周旋于丈席。则其商也岂徒利也。教亦在其中矣。
与金三山
深川告诀。不能执绋以先后。势固使然。而诚礼蔑如。俯仰增恧。窃惟庐下哀毁既甚。重以脩途奉柩。岂其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7L 页
 无添损耶。远不任贡虑之至。襄礼谓尝择以今月二十二日矣。元礼书来。始知趁卜于十四。鼎焕适有亲忧。末由趍圹诀。远外穷天之恸。尤无以为喻也。未知寿藏抑石室旧麓耶。或别占新阡否。启圹而土色何如。会者又几何人也。种种悲溯。不能自已也。噫渼上读书之会。何时得复见耶。我东沙溪之家。慎翁再传其道。而当时从游诸君子。以所事老先师者事之。则吾辈之期望于庐下。岂有异同也。且先生著述。异时不朽之托。舍庐下而伊谁哉。更乞为道自爱。无至过哀伤生。则斯文幸甚。先师语录问答。仆亦辑成一册。同门诸公。各以所记。来聚则增删为言行录。恐未为不可也。
无添损耶。远不任贡虑之至。襄礼谓尝择以今月二十二日矣。元礼书来。始知趁卜于十四。鼎焕适有亲忧。末由趍圹诀。远外穷天之恸。尤无以为喻也。未知寿藏抑石室旧麓耶。或别占新阡否。启圹而土色何如。会者又几何人也。种种悲溯。不能自已也。噫渼上读书之会。何时得复见耶。我东沙溪之家。慎翁再传其道。而当时从游诸君子。以所事老先师者事之。则吾辈之期望于庐下。岂有异同也。且先生著述。异时不朽之托。舍庐下而伊谁哉。更乞为道自爱。无至过哀伤生。则斯文幸甚。先师语录问答。仆亦辑成一册。同门诸公。各以所记。来聚则增删为言行录。恐未为不可也。与李中洲
少也随执事后。听讲于云楼丈席。便隔前尘影事。虽相对于今日。而鬓发皆皤然。犹不辨其某谁。况别后光阴。已过四十馀载。安保其必记少时游也。先师在时。每奖执事曰心静者识明。到今追惟。执事晚年成德。蔚然有山斗之望。而四方矜式。使先师之道。不坠于地。则先师当日之奖。此其验欤。仄闻执事就养于令胤官中。此亦 圣恩攸暨。惟愿为道保重。且奖进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8H 页
 后学。以报不报之恩。则此虽老而不学。可以摄衣周旋于广寒楼上矣。
后学。以报不报之恩。则此虽老而不学。可以摄衣周旋于广寒楼上矣。与李中洲
李友由则还。获拜下复书。盥读以还。穷巷生色。又况见奖过隆。执礼太恭。令人不敢当也。执事齿德俱隆。圣上礼之以宾师。多士望之如山斗。则何其降屈威尊。乃称弟于文字之间耶。弟之一字。地丑则言之。德齐则书之。而执事士林之宗匠也。不佞山野之老圃也。其高下贤愚。若是悬绝。而反得此千万不近似之称于书牍之中。则执事虽有谦恭下士之德。而不佞何堪此不称情之题目耶。揆之私分。荣幸则极矣。而旋切惶缩不自安也。书后忽已春生。伏惟殊方换岁。道体茂纳洪休。德学俱进。尤不胜仰颂。鼎焕学无分寸之进。居然作七耋人。因感朱夫子所赠吕伯恭之言曰功夫易间断。义理难推寻。岁月如流。甚可忧叹。晦翁尚然。况吾辈碌碌鄙人者乎。栗翁之训曰一毫不及圣人。是吾事未了。此非徒先辈之自期如此。虽如执事之盛德。亦自反而警策也。先圣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束脩已上。吾未尝无诲焉。圣人之学。不待加勉。而又复不倦于教。则束脩于宫墙者。殆不知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8L 页
 几千人也。仄闻执事门庭。岂曰无执贽请业之士。而一向谢遣。则后生小子。于何观感而考德耶。窃恐执事之学。不免于厌。而教亦从此而倦也。岂非栗翁所道吾事未了者欤。区区所望于执事者。以圣人自期。不倦于诲人。则愚虽老而不学。亦不惮于就正也。呜呼。云楼寂矣。秋水寒矣。顾瞻今世。山林宿望。渊源旧学。舍执事其谁也。他日束脩而请业。其名有在修者。即吾儿也。一依古人易子之教。而且续先师旧业。则其为感荷。尤如何哉。近看大学。或有自得处。劄成一册子。非远书一一可质。而其曰古之欲明明德章。古之二字。盖言今之不然。而愚则曰虞典曰若稽古。帝尧之意也。其曰克明峻德者。修身已上之事也。以亲九族者。齐家之事也。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者。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推是以观。则八条之次第。皆从虞典中来。三纲领亦在其中。而所谓尧典大学之祖宗者。非是之谓欤。不敢自是。玆以禀质焉。
几千人也。仄闻执事门庭。岂曰无执贽请业之士。而一向谢遣。则后生小子。于何观感而考德耶。窃恐执事之学。不免于厌。而教亦从此而倦也。岂非栗翁所道吾事未了者欤。区区所望于执事者。以圣人自期。不倦于诲人。则愚虽老而不学。亦不惮于就正也。呜呼。云楼寂矣。秋水寒矣。顾瞻今世。山林宿望。渊源旧学。舍执事其谁也。他日束脩而请业。其名有在修者。即吾儿也。一依古人易子之教。而且续先师旧业。则其为感荷。尤如何哉。近看大学。或有自得处。劄成一册子。非远书一一可质。而其曰古之欲明明德章。古之二字。盖言今之不然。而愚则曰虞典曰若稽古。帝尧之意也。其曰克明峻德者。修身已上之事也。以亲九族者。齐家之事也。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者。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推是以观。则八条之次第。皆从虞典中来。三纲领亦在其中。而所谓尧典大学之祖宗者。非是之谓欤。不敢自是。玆以禀质焉。与李中洲
臣民多福。 元子诞降。喜甚无寐。张子先我获也。仄闻令胤移符于湖南之茂朱。执事行窝。亦从近移就于山水窟宅。晚来清福。何必炼丹砂于句漏。令人欲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9H 页
 飘飘羽化于建标楼上。与之论仙诀。而恨无由也。伏惟道体神相万重。啸咏之暇。剩得二水三山之乐。何等献贺之至。鼎焕少时一登寒风唤睡之间。做了半日之趣。而只恨所挟之无敌此境界。今幸丈席密迩来临。非惟南士之饱饫德义。烟云草木。亦将有光华者也耶。鼎焕前月初。奄见长孙妇冤逝。痛悼不可言。自此闺门细琐。无可付处。奈何柰何。此距仙乡。不过一宿可到。顾此筋力。亦可以自强。倘不及此承诲。则年迫七耋。馀龄无多此世。而末由究先师绪业。岂非遗恨者欤。初欲送子受业。以续渊源之好。而来书谓亲戚故旧之外。不得引接宾客。盛教如此。则不敢复有馀望。然至若同门故旧。恐不在此科。又岂有取憾于他人也耶。曾献经说禀目。迄未承答。似缘匆挠无暇之致也。更乞逐条批回。以慰孤陋。则何幸如之。大率心者理之所会之地。而不可单言气也。偶有所咏。玆又禀呈。如有病处。幸加增削而赐和不敢望也。
飘飘羽化于建标楼上。与之论仙诀。而恨无由也。伏惟道体神相万重。啸咏之暇。剩得二水三山之乐。何等献贺之至。鼎焕少时一登寒风唤睡之间。做了半日之趣。而只恨所挟之无敌此境界。今幸丈席密迩来临。非惟南士之饱饫德义。烟云草木。亦将有光华者也耶。鼎焕前月初。奄见长孙妇冤逝。痛悼不可言。自此闺门细琐。无可付处。奈何柰何。此距仙乡。不过一宿可到。顾此筋力。亦可以自强。倘不及此承诲。则年迫七耋。馀龄无多此世。而末由究先师绪业。岂非遗恨者欤。初欲送子受业。以续渊源之好。而来书谓亲戚故旧之外。不得引接宾客。盛教如此。则不敢复有馀望。然至若同门故旧。恐不在此科。又岂有取憾于他人也耶。曾献经说禀目。迄未承答。似缘匆挠无暇之致也。更乞逐条批回。以慰孤陋。则何幸如之。大率心者理之所会之地。而不可单言气也。偶有所咏。玆又禀呈。如有病处。幸加增削而赐和不敢望也。与李中洲
向来复札。迨极披慰。伏惟阳生。道体康宁。日用动静。想有与阳俱长之益。尤不任仰慰之挚。顾此无状。居然作七耋人。年进学退。恐终为无闻之鬼。奈何奈何。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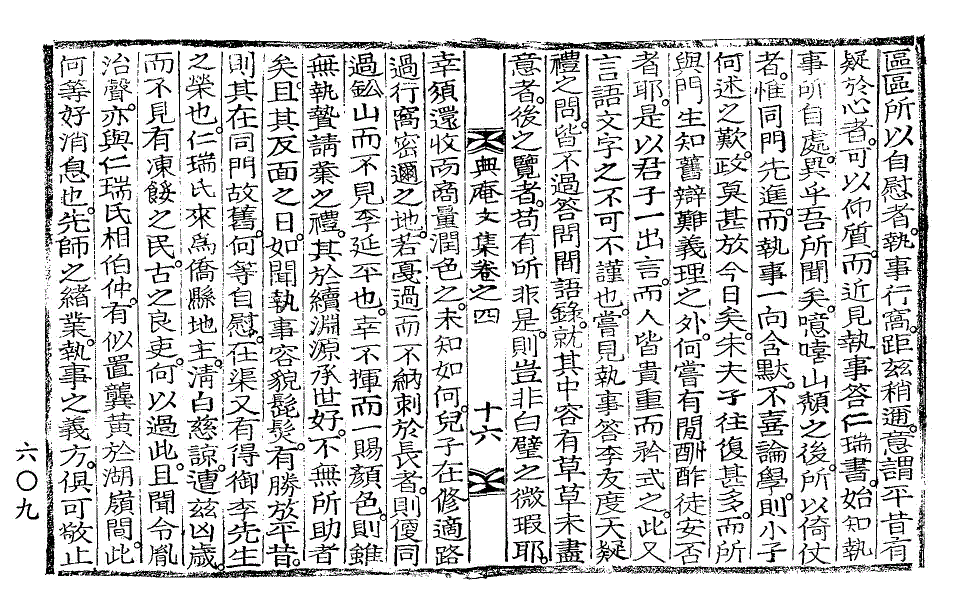 区区所以自慰者。执事行窝。距玆稍迩。意谓平昔有疑于心者。可以仰质。而近见执事答仁瑞书。始知执事所自处。异乎吾所闻矣。噫嘻山颓之后。所以倚仗者。惟同门先进。而执事一向含默。不喜论学。则小子何述之叹。政莫甚于今日矣。朱夫子往复甚多。而所与门生知旧辩难义理之外。何尝有閒酬酢徒安否者耶。是以君子一出言。而人皆贵重而矜式之。此又言语文字之不可不谨也。尝见执事答李友度天疑礼之问。皆不过答问间语录。就其中容有草草未尽意者。后之览者。苟有所非是。则岂非白璧之微瑕耶。幸须还收而商量润色之。未知如何。儿子在修适路过行窝密迩之地。若戛过而不纳刺于长者。则便同过铅山而不见李延平也。幸不挥而一赐颜色。则虽无执贽请业之礼。其于续渊源承世好。不无所助者矣。且其反面之日。如闻执事容貌髭发。有胜于平昔。则其在同门故旧。何等自慰。在渠又有得御李先生之荣也。仁瑞氏来为侨县地主。清白慈谅。遭玆凶岁。而不见有冻馁之民。古之良吏。何以过此。且闻令胤治声。亦与仁瑞氏相伯仲。有似置龚黄于湖岭间。此何等好消息也。先师之绪业。执事之义方。俱可敬止
区区所以自慰者。执事行窝。距玆稍迩。意谓平昔有疑于心者。可以仰质。而近见执事答仁瑞书。始知执事所自处。异乎吾所闻矣。噫嘻山颓之后。所以倚仗者。惟同门先进。而执事一向含默。不喜论学。则小子何述之叹。政莫甚于今日矣。朱夫子往复甚多。而所与门生知旧辩难义理之外。何尝有閒酬酢徒安否者耶。是以君子一出言。而人皆贵重而矜式之。此又言语文字之不可不谨也。尝见执事答李友度天疑礼之问。皆不过答问间语录。就其中容有草草未尽意者。后之览者。苟有所非是。则岂非白璧之微瑕耶。幸须还收而商量润色之。未知如何。儿子在修适路过行窝密迩之地。若戛过而不纳刺于长者。则便同过铅山而不见李延平也。幸不挥而一赐颜色。则虽无执贽请业之礼。其于续渊源承世好。不无所助者矣。且其反面之日。如闻执事容貌髭发。有胜于平昔。则其在同门故旧。何等自慰。在渠又有得御李先生之荣也。仁瑞氏来为侨县地主。清白慈谅。遭玆凶岁。而不见有冻馁之民。古之良吏。何以过此。且闻令胤治声。亦与仁瑞氏相伯仲。有似置龚黄于湖岭间。此何等好消息也。先师之绪业。执事之义方。俱可敬止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0H 页
 不已。
不已。答李杜谷
来谕明德有分数。如格诚正修。皆所以变化其有分数之气质。尽复其无分数之性理者。愚见亦如此矣。愚之前所道不言明之者之有分数者。非敢斥高明之论。而合下文义。有所听莹而然也。执事谓明德有分数。恐亦有些语病也何者。不曰明明德者有分数。而辄云明德有分数。故往往有文义未彰之病矣。不及见上面所證。而只见下面此段。则岂无愚生之惑耶。大率圣凡之明德。言其本然之理。则初未尝不同。所谓舜蹠皆一性也。舜之为舜。禀其清明纯粹之气。故明德自明。蹠之为蹠。禀其浊驳昏暗之气。故明德不明。而苟以善自治。则岂非程子所谓虽昏愚之至。皆可渐磨而进。而彼乃自绝于天。则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此岂明德之罪耶。横渠之训曰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别。厚者可以开而开之也难。薄者开之也易。开则达于天道。与圣人一也。推是而言则明德本无分数。而明之者有分数也。向因慎晦叔获玩执事所为众人明德图。则以黑暗为圈子。就黑暗中为一小白圈子。分书清浊粹驳。虚灵不昧等字。此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0L 页
 出于虚灵有优劣之论。而未知众人方寸。若是其黑暗。终无变化气质之时。而与禽兽之不能变化者。一体同归也哉。愚之所为明德图。圣凡通为一图。而但气质自有不齐之分。谨玆呈上。笑领而可否之也。来谕若以栗翁虚灵优劣之论为误。而攻之则或可也者。执事口气。容有为人莫己若之病矣。沙溪虽亲承栗翁之学。而于文义有所不合。则犹有不能遵守之教。然至于虚灵有优劣之教。此金振纲之所录。而非栗谷之手录也。栗翁曰心志则可以变愚为智。变不肖为贤。此则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故也。若有优劣。则愚不可以变智。不肖难以为贤矣。何以知其然也。击蒙要诀曰人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故也。推是以言。则其曰虚灵优劣者。乃记录之误也。然善观则非若执事所云众人明德之黑窣窣而无复变化也。盖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心也者。程子之训。而朱子又释之曰既发则不可谓非心。但有不善则恐非心之本体也。推是以究则虚灵底虽有优劣。而拘于气而然也。非虚灵之本体然也。朱子所谓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者。乃虚灵之本体也。而至于气质所拘。人欲所蔽。有时而
出于虚灵有优劣之论。而未知众人方寸。若是其黑暗。终无变化气质之时。而与禽兽之不能变化者。一体同归也哉。愚之所为明德图。圣凡通为一图。而但气质自有不齐之分。谨玆呈上。笑领而可否之也。来谕若以栗翁虚灵优劣之论为误。而攻之则或可也者。执事口气。容有为人莫己若之病矣。沙溪虽亲承栗翁之学。而于文义有所不合。则犹有不能遵守之教。然至于虚灵有优劣之教。此金振纲之所录。而非栗谷之手录也。栗翁曰心志则可以变愚为智。变不肖为贤。此则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故也。若有优劣。则愚不可以变智。不肖难以为贤矣。何以知其然也。击蒙要诀曰人之虚灵。不拘于禀受故也。推是以言。则其曰虚灵优劣者。乃记录之误也。然善观则非若执事所云众人明德之黑窣窣而无复变化也。盖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心也者。程子之训。而朱子又释之曰既发则不可谓非心。但有不善则恐非心之本体也。推是以究则虚灵底虽有优劣。而拘于气而然也。非虚灵之本体然也。朱子所谓虚灵不昧。具众理应万事者。乃虚灵之本体也。而至于气质所拘。人欲所蔽。有时而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1H 页
 昏。则有能明之者优也。有不能明之者劣也。及夫明其明德。则劣者变而至优也。岂可断然以优劣一定而不移哉。至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者。盖谓圣人以天命之性为实。孟子所谓性善是也。释氏不知本心之理出于天命。而反以天命为虚不用。辛苦修行者是也。然则儒释之所以不同者。我实而彼虚。我以仁义而彼以慈悲。我以无妄而彼以寂灭也。愚何尝合而为一者耶。至若人物性同不同之论。执事欲执二者之中而救其末流之弊。其论得矣。然其曰五性全具。人物皆同者。周子太极图已具焉。朱子释之曰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则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则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也。朱子又为之论曰万物之生。同一太极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此理字。即伊川所谓性即理也之意也。或者每以谓理与性不同。然太极图中训理处。皆以性字释之。然则
昏。则有能明之者优也。有不能明之者劣也。及夫明其明德。则劣者变而至优也。岂可断然以优劣一定而不移哉。至若圣人本天。释氏本心者。盖谓圣人以天命之性为实。孟子所谓性善是也。释氏不知本心之理出于天命。而反以天命为虚不用。辛苦修行者是也。然则儒释之所以不同者。我实而彼虚。我以仁义而彼以慈悲。我以无妄而彼以寂灭也。愚何尝合而为一者耶。至若人物性同不同之论。执事欲执二者之中而救其末流之弊。其论得矣。然其曰五性全具。人物皆同者。周子太极图已具焉。朱子释之曰自男女而观之则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极也。自万物而观之则万物各一其性。而万物一太极也。盖合而言之则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则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也。朱子又为之论曰万物之生。同一太极也。而谓其各具。则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夺。此统之所以有宗。会之所以有元也。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此理字。即伊川所谓性即理也之意也。或者每以谓理与性不同。然太极图中训理处。皆以性字释之。然则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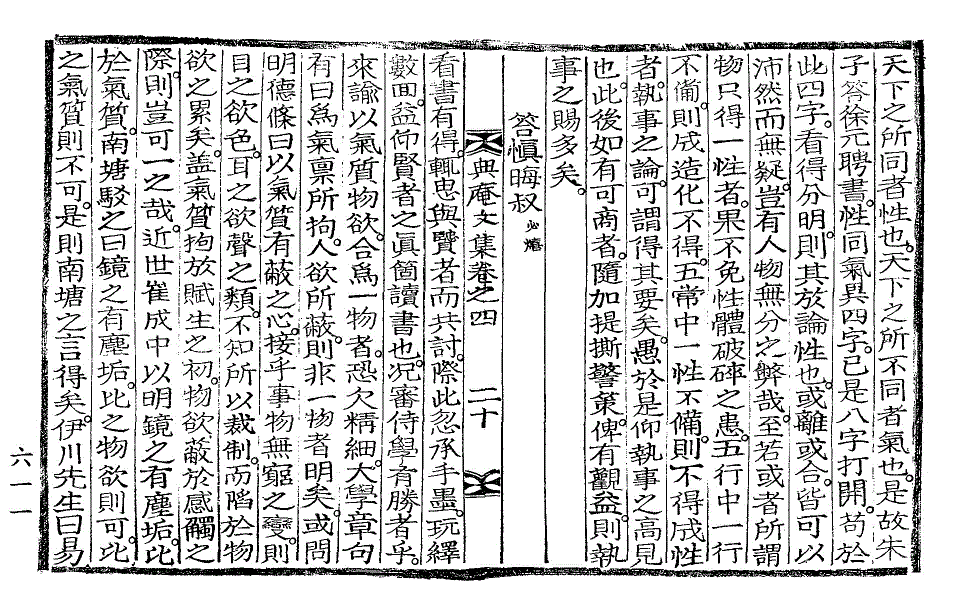 天下之所同者性也。天下之所不同者气也。是故朱子答徐元聘书。性同气异四字。已是八字打开。苟于此四字。看得分明。则其于论性也。或离或合。皆可以沛然而无疑。岂有人物无分之弊哉。至若或者所谓物只得一性者。果不免性体破碎之患。五行中一行不备。则成造化不得。五常中一性不备。则不得成性者。执事之论。可谓得其要矣。愚于是仰执事之高见也。此后如有可商者。随加提撕警策。俾有观益。则执事之赐多矣。
天下之所同者性也。天下之所不同者气也。是故朱子答徐元聘书。性同气异四字。已是八字打开。苟于此四字。看得分明。则其于论性也。或离或合。皆可以沛然而无疑。岂有人物无分之弊哉。至若或者所谓物只得一性者。果不免性体破碎之患。五行中一行不备。则成造化不得。五常中一性不备。则不得成性者。执事之论。可谓得其要矣。愚于是仰执事之高见也。此后如有可商者。随加提撕警策。俾有观益。则执事之赐多矣。答慎晦叔(必熺)
看书有得。辄思与贤者而共讨。际此忽承手墨。玩绎数回。益仰贤者之真个读书也。况审侍学有胜者乎。来谕以气质物欲。合为一物者。恐欠精细。大学章句有曰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非一物者明矣。或问明德条曰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目之欲色。耳之欲声之类。不知所以裁制。而陷于物欲之累矣。盖气质拘于赋生之初。物欲蔽于感触之际。则岂可一之哉。近世崔成中以明镜之有尘垢。比于气质。南塘驳之曰镜之有尘垢。比之物欲则可。比之气质则不可。是则南塘之言得矣。伊川先生曰易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2H 页
 所谓继之者善也者。即性之谓也。水之有清浊。犹性之有善恶。彼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清浊宝珠之谕。从此说中来。推是论之。则清浊水中宝珠。不可唤做气质所拘。亦不可唤做物欲所蔽也。善固性也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则圣人不待清而自清。宝珠之在清水者也。凡愚则流而渐浊。宝珠之在浊水者也。是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随其用力之迟缓勇怠。而浊变为清。则却只是元初水也。而又元初宝珠也。水之清珠之宝。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又不是清与浊。在水中与宝珠对。各流出也。愚见如是。而贤者恐未喻。来谕杂糅二字。不可著之于天地之前。亦不可著之于天地之后者。似说得伤怏。天地万物之前。固不可言杂糅。而天地万物之后。气同而理异。则气之所禀。不能无清浊纯驳之不齐。禀是气之清明者为圣为贤。禀是气之昏浊者为凡为愚。而及其变化气质也。浊者为清。凡者为贤。此在用功如何。岂可不用其力而见其湛一之本然耶。至若气
所谓继之者善也者。即性之谓也。水之有清浊。犹性之有善恶。彼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清浊宝珠之谕。从此说中来。推是论之。则清浊水中宝珠。不可唤做气质所拘。亦不可唤做物欲所蔽也。善固性也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则圣人不待清而自清。宝珠之在清水者也。凡愚则流而渐浊。宝珠之在浊水者也。是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随其用力之迟缓勇怠。而浊变为清。则却只是元初水也。而又元初宝珠也。水之清珠之宝。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又不是清与浊。在水中与宝珠对。各流出也。愚见如是。而贤者恐未喻。来谕杂糅二字。不可著之于天地之前。亦不可著之于天地之后者。似说得伤怏。天地万物之前。固不可言杂糅。而天地万物之后。气同而理异。则气之所禀。不能无清浊纯驳之不齐。禀是气之清明者为圣为贤。禀是气之昏浊者为凡为愚。而及其变化气质也。浊者为清。凡者为贤。此在用功如何。岂可不用其力而见其湛一之本然耶。至若气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2L 页
 质之非心。则愚已辨之矣。盛论偶与鄙见吻合。更何叠床耶。圣凡气质。有万不同。则气质之有分数固也。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杜谷所谓明德有分数之说。不知众人之蔽于欲而自绝于天命也。学而至变化气质。则天命之本体。自然呈露。方此时也。又岂有分数者乎。向因转递辨明之。安保其不洪乔耶。来谕末段。益见其用功亲切。寒水先生曰万物之理。虽不可不穷。而比诸日用行事。犹为不紧。此有德之训也。大率不有涵养本原之功。而遽说性说理者。不为下学而欲上达者也。自今就涵养居敬之功。相与考其进退。岂非相观而相益者耶。
质之非心。则愚已辨之矣。盛论偶与鄙见吻合。更何叠床耶。圣凡气质。有万不同。则气质之有分数固也。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杜谷所谓明德有分数之说。不知众人之蔽于欲而自绝于天命也。学而至变化气质。则天命之本体。自然呈露。方此时也。又岂有分数者乎。向因转递辨明之。安保其不洪乔耶。来谕末段。益见其用功亲切。寒水先生曰万物之理。虽不可不穷。而比诸日用行事。犹为不紧。此有德之训也。大率不有涵养本原之功。而遽说性说理者。不为下学而欲上达者也。自今就涵养居敬之功。相与考其进退。岂非相观而相益者耶。答慎晦叔
蝉声益清。尽有怀伯恭底意。料襮先施手墨。满幅娓娓。可想其心得之馀。因审侍学增重。尤何等远慰。来谕槩是。而鄙说之分气质物欲为清浊。盖因贤者所谓气质物欲。一而二二而一也而发也。虽然此非愚之臆对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是性也。何尝不善。但气之为物。有清明昏浊之异。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之未纯。且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则为贤。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3H 页
 气浊欲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此岂非圣凡之分清浊。为气质物欲之證耶。盖气质物欲。有分言之者。有合言之者。朱子曰性则水之静。情则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泛滥者也。才则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才者气质也。欲者物欲也。此岂非合而言者耶。至若合清浊为性之喻。则朱子曰性比之水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污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污浊。猝难便清。故煞用气力。然后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岂非清浊为性之喻乎。且夫未发之时。用诚意正心之工者。非愚之刱说也。朱子与张钦夫书曰。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又与何叔京书曰未发之前。太极之静而阴也。已发之后。太极之动而阳也。其未发也。敬为之主而义已具。其已发也。必主于义而敬行焉。南塘记问录曰孔子曰敬而直内。内直则未发矣。大学曰正心。心正则未发矣。继之曰孔子曾子以未发工夫言。由是推之则周子所谓圣人定之以中
气浊欲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此岂非圣凡之分清浊。为气质物欲之證耶。盖气质物欲。有分言之者。有合言之者。朱子曰性则水之静。情则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泛滥者也。才则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才者气质也。欲者物欲也。此岂非合而言者耶。至若合清浊为性之喻。则朱子曰性比之水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污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污浊。猝难便清。故煞用气力。然后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岂非清浊为性之喻乎。且夫未发之时。用诚意正心之工者。非愚之刱说也。朱子与张钦夫书曰。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又与何叔京书曰未发之前。太极之静而阴也。已发之后。太极之动而阳也。其未发也。敬为之主而义已具。其已发也。必主于义而敬行焉。南塘记问录曰孔子曰敬而直内。内直则未发矣。大学曰正心。心正则未发矣。继之曰孔子曾子以未发工夫言。由是推之则周子所谓圣人定之以中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3L 页
 正仁义者。亦未发工夫也。苟不静存于未发之前。则何以动察于已发之后耶。子思所谓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亦未发前工夫也。故章句曰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皆未发之谓也。程子尝讥许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之非。若必以未发时。无所敬畏。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此后学之不可不知也。惟愿贤者更加存养于未发之前。以为已发后省察之验。则岂非朋友间互有相益者耶。至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也。以是推之则形而上。虽曰谓之道也。而器亦在其中也。何以明其然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盖阴阳乃形而下之器也。而其所以为阴阳则道也。道者理也。器者气也。大率理与气。元不相离。理无气外之理。气无理外之气。程子曰元亨。是气之方行而未著于物也。是上一截事。继之者善也。利贞。是气之结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成之者性也。以言乎元亨之气方行而未著于物则谓之道也。而气亦行于其中。虽谓之形而上。理寓于气可也。以言乎利贞之气。结成一物。则亦谓之器也。而道已行于那里。虽谓之形而下。气
正仁义者。亦未发工夫也。苟不静存于未发之前。则何以动察于已发之后耶。子思所谓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亦未发前工夫也。故章句曰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皆未发之谓也。程子尝讥许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曷尝有如此圣人。又每力诋坐禅入定之非。若必以未发时。无所敬畏。则又安可讥许渤而非入定哉。此后学之不可不知也。惟愿贤者更加存养于未发之前。以为已发后省察之验。则岂非朋友间互有相益者耶。至若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也。以是推之则形而上。虽曰谓之道也。而器亦在其中也。何以明其然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盖阴阳乃形而下之器也。而其所以为阴阳则道也。道者理也。器者气也。大率理与气。元不相离。理无气外之理。气无理外之气。程子曰元亨。是气之方行而未著于物也。是上一截事。继之者善也。利贞。是气之结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成之者性也。以言乎元亨之气方行而未著于物则谓之道也。而气亦行于其中。虽谓之形而上。理寓于气可也。以言乎利贞之气。结成一物。则亦谓之器也。而道已行于那里。虽谓之形而下。气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4H 页
 合于道亦可也。愚之此说。自器亦道道亦器中推而得之也。贤者熟思而更示之如何。杜谷所为众人明德黑圈图。以物之不能开塞言之。则图似然矣。而岂可曰众人之明德。如是黑暗者耶。众人虽有气质之拘物欲之累。而变以化之则浊者可变而之清。驳者可变而之粹。而若是黑暗则终无变黑暗为清明之时矣。闻之师。明德者心性所具之理。而岂可以气质者当之哉。心虽属于气也。而灵处是心。故朱子曰心即气之精爽。又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尤灵。由是言之则方寸之间。虚灵洞澈。万理咸备者。是心之体也。何可专以气质之有昏明强弱论之哉。贤者以圣凡明德。合成一图。大槩得之。而浊字书于圆圈之上面者。异乎朱子所谓清底在上。浊底在下之意也。喜怒哀乐未发。气不用事。盖此时恶自沉在下面。以此言之则清字书于上面。浊字书于下面。似或然矣。退溪作天命图。盖取太极图说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即所谓形既生矣。左气阳之为。即所谓神发知矣。依此之例分书气质于圈上。似圆满矣。退翁岂欺我哉。
合于道亦可也。愚之此说。自器亦道道亦器中推而得之也。贤者熟思而更示之如何。杜谷所为众人明德黑圈图。以物之不能开塞言之。则图似然矣。而岂可曰众人之明德。如是黑暗者耶。众人虽有气质之拘物欲之累。而变以化之则浊者可变而之清。驳者可变而之粹。而若是黑暗则终无变黑暗为清明之时矣。闻之师。明德者心性所具之理。而岂可以气质者当之哉。心虽属于气也。而灵处是心。故朱子曰心即气之精爽。又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尤灵。由是言之则方寸之间。虚灵洞澈。万理咸备者。是心之体也。何可专以气质之有昏明强弱论之哉。贤者以圣凡明德。合成一图。大槩得之。而浊字书于圆圈之上面者。异乎朱子所谓清底在上。浊底在下之意也。喜怒哀乐未发。气不用事。盖此时恶自沉在下面。以此言之则清字书于上面。浊字书于下面。似或然矣。退溪作天命图。盖取太极图说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即所谓形既生矣。左气阳之为。即所谓神发知矣。依此之例分书气质于圈上。似圆满矣。退翁岂欺我哉。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4L 页
 答慎晦叔
答慎晦叔前书所谓美恶杂糅之气。不可著之于天地之先。亦不可著之于人物之后者。盖指人物方生之初也。朱子曰阴阳循环如磨。游气纷扰。如磨中出者。易曰强柔相摩。八卦相荡者。阴阳之循环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游气之纷扰也。由是观之。则太极只在阴阳之中。而非能离阴阳也。其所谓阴阳循环者。正如面磨相似。其四边只管层层撒出。天地之气。运转无已。只管散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精。粗者为物。精者为人。所以有偏正精粗之分。张子所谓合而成质。生人物之万殊者此也。以言乎游气纷扰者。在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时。则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盖于此时。只有成男成女之凝。而未及化生人物。以此推之。则虽圣贤。就游气纷扰之中。得其至精至正之气而生者也。程子所谓精一者。间或值之。而至于众万之生。就游气纷扰中。禀其或粗或细或偏或正。参差不齐之气而生出者。益参差不齐矣。贤者所谓吾人方生之初者。想亦不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此游气纷扰之意也。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便是继之者善也。盖所谓继之者善也者。造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5H 页
 化流行。万物方资以始而未实也。其曰万物生生者。物生已实。造化与物。各藏其用而无所为也。盖所谓成之者性也。前答有所未尽。故今复及之。未知盛见以为如何。
化流行。万物方资以始而未实也。其曰万物生生者。物生已实。造化与物。各藏其用而无所为也。盖所谓成之者性也。前答有所未尽。故今复及之。未知盛见以为如何。答慎晦叔太极图问目
前书阴根阳阳根阴而指其本体也。(止。)所谓本体者何也。阴之本体是动。而阳之本体是静耶。以互根为本体。而释此本字。其义恐凿。
此无极而太极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观其图解则动静阴阳。互为其根。就其图而言之则指其本体之意。如视诸掌。贤者之疑。政所谓不当疑而疑者矣。盍观于图。
五气交运者。形而上者也。益参差者。形而下者也。(止。)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则以交运参差。分作两截。而一属形上。一属形下。尤未知如何。
五气交运者。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形而上者也。非不知理之为形上。而盖谓人物未生之前。便同三代以前之意也。益参差者。二五之气。清浊粹驳。赋于人而有万不齐。故形而下者也。盖言人物已生之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5L 页
 后。便同三代以后之意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理为体而气为用也。故理中有气。是形上者也。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气化者为体而理之发为用。故气中有理。是形下者也。然则交运者。是赋生之前。而理未尝不在其中也。参差者。又是赋生之时。而气未尝不属这里也。惟其如是。则参差与益参差。岂无等分时节耶。参差者气异也。益参差者理绝不同也。贤者每以参差与益参差。看作一等时节。愚未知其其然也。
后。便同三代以后之意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则理为体而气为用也。故理中有气。是形上者也。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气化者为体而理之发为用。故气中有理。是形下者也。然则交运者。是赋生之前。而理未尝不在其中也。参差者。又是赋生之时。而气未尝不属这里也。惟其如是。则参差与益参差。岂无等分时节耶。参差者气异也。益参差者理绝不同也。贤者每以参差与益参差。看作一等时节。愚未知其其然也。太极之阴阳动静。互为其根。则岂有本不同之理耶。(止。)动静之间。何者是阳。何者是阴耶。阴阳动静。终恐同归于一物。而不得有二名。
朱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推之于前。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不见其终之离。其所以动中之静静中之动。未尝一息而间断。则其本体之妙。虽鬼神莫测其端倪。真所谓本混融而无间也。动而不能无静。犹静而不能无动。静而涵动之所本。动而见静之所存。则其理未尝不同矣。
阳变阴合。生水火木金土。则岂非万物化生。各一其性耶。(止。)今以五行之生。便作万物之生。此其一疑也。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6H 页
 五行之生。各其一性一也。而儿辈传写之际。便以万物化生四字书之。此则记录之谬也。
五行之生。各其一性一也。而儿辈传写之际。便以万物化生四字书之。此则记录之谬也。交运益参差。證之于顺布者可乎。既曰益参差则与顺布者不称。(止。)一阴阳之初。动静已自参差。而交五气之际。益有参差。
盖二气交运者。图说所谓二气交感之时。则化生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五气顺布者。在于二气交感之前。则水火木金土者。阴阳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阴阳五行。循环相因。则当此时节。其气也顺布。其时也顺行。及是之时。一有不顺。则五行失序。而木不得生火。火不得生土。土不得生金。金不得生水。水不得生木。四时失序。而春不得为春。夏不得为夏。秋不得为秋。冬不得为冬矣。然则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之际。造化之妙。有顺无差。而至于万物赋生之时。刚柔美恶。有万不齐。则合下参差者。至此而益参差矣。然太极之理。则岂可以参差论耶。但其所禀之气。有偏正之不同。人得正且通。物得偏且塞。周子所谓善恶分矣。而朱子所谓隔于气而物不能知。人不能存。是皆自绝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也。且以图说所谓五性感动而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6L 页
 善恶分之义观之。则其所分善恶而益参差者。指其五性感动之前可乎。指其五性感动之际可乎。通书所谓诚无为者太极也。几善恶者阴阳也。德曰仁义礼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图上说来。则天地万物阴阳五行。莫不具太极。而其各具一太极处。又便有许多道理。须要随处尽得。则大学明德。岂益参差不齐而有分数耶。愚则曰益参差者。在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焉之际。则明德之本体。不在于益参差之间矣。昔彪德远曰天命惟人得之。而物无所与。(近世湖论原于此。)朱子曰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而生者也。然岂离乎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观其人物生生不穷。则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见矣。然则人物所受之外。岂别有全体太极者耶。所谓益参差者。其不在于隔于气者耶。彼其隔于气而益参差不齐者。盖谓自绝于天。而非明德之有分数者也。
善恶分之义观之。则其所分善恶而益参差者。指其五性感动之前可乎。指其五性感动之际可乎。通书所谓诚无为者太极也。几善恶者阴阳也。德曰仁义礼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图上说来。则天地万物阴阳五行。莫不具太极。而其各具一太极处。又便有许多道理。须要随处尽得。则大学明德。岂益参差不齐而有分数耶。愚则曰益参差者。在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焉之际。则明德之本体。不在于益参差之间矣。昔彪德远曰天命惟人得之。而物无所与。(近世湖论原于此。)朱子曰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而生者也。然岂离乎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观其人物生生不穷。则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见矣。然则人物所受之外。岂别有全体太极者耶。所谓益参差者。其不在于隔于气者耶。彼其隔于气而益参差不齐者。盖谓自绝于天。而非明德之有分数者也。杂糅。證之于真精妙合可乎。既曰杂糅则真精者不合。(止。)真虽无人与物之异。而精必有人与物之不同。不然理同而气亦同矣。人与物之分。顾安在哉。
图说所谓无极之真者理也。理与气妙合而凝。则乾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7H 页
 道成男。坤道成女。岂非至真至精者耶。自其一原而观之则理同而气异也。自其异体而观之则气同而理异也。然则其曰杂糅者。言之于异体之时。而不当言于一原真精之时。是故杂糅者。人物之禀赋。偏正纯驳有万不齐也。朱子曰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惟其如是。则无妄不二。与杂糅二字。同乎异乎。图说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则物之得其塞而不通。盖可见矣。当此时节。人物之气。或杂或糅。则真也精也。可言于未赋之前。而杂也糅也。当言于已赋之时矣。
道成男。坤道成女。岂非至真至精者耶。自其一原而观之则理同而气异也。自其异体而观之则气同而理异也。然则其曰杂糅者。言之于异体之时。而不当言于一原真精之时。是故杂糅者。人物之禀赋。偏正纯驳有万不齐也。朱子曰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惟其如是。则无妄不二。与杂糅二字。同乎异乎。图说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则物之得其塞而不通。盖可见矣。当此时节。人物之气。或杂或糅。则真也精也。可言于未赋之前。而杂也糅也。当言于已赋之时矣。来谕真精妙合。化生万物下细注曰。此即人物方生之时云云。贤者不见辨疑所谓沙溪之说乎。沙溪曰尝见栗谷也。先生论太极图说。至朱子解妙合而凝曰。本混融而无间也。极赞美之。愚曾误认人物始生之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及闻先生之言。乃知前见之误也。推是言之。则贤者所注人物方生之时者。其可乎。更细思而示破也。
答郑正甫(就毅)
牙山解携。漠然若始不相识者久矣。春中为探丈席安候。更游稽山馆中。兼受中庸一部。日与明师益友。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7L 页
 上下讨论。而只恨座上无吾正甫兄弟者。扬其袂说义理也。秋间仍培春递。获拜先施下状。其为披豁。殆不减羾寒而濯清也。书后天气向寒。侍履增吉。联床讲讨。怡怡以为乐也耶。鼎焕粗保宿状。而旧学荒废。了无寸进。有时怵然复寻尘蠹。而读未数编。欠伸思睡。旋不免束之高架。此其前却者之习。良可叹也。仲氏竹溪之筑。其勇甚快。想与明叟辈。源源讲论于溥川之上。洒然有胥得之趣。而顾此无状。屏居穷山。无由侧听其绪馀。孤陋之憾。愈往愈甚也。只乞足下时赐德音。以警聋瞽之一二。则其所补益。何必相面而后足耶。
上下讨论。而只恨座上无吾正甫兄弟者。扬其袂说义理也。秋间仍培春递。获拜先施下状。其为披豁。殆不减羾寒而濯清也。书后天气向寒。侍履增吉。联床讲讨。怡怡以为乐也耶。鼎焕粗保宿状。而旧学荒废。了无寸进。有时怵然复寻尘蠹。而读未数编。欠伸思睡。旋不免束之高架。此其前却者之习。良可叹也。仲氏竹溪之筑。其勇甚快。想与明叟辈。源源讲论于溥川之上。洒然有胥得之趣。而顾此无状。屏居穷山。无由侧听其绪馀。孤陋之憾。愈往愈甚也。只乞足下时赐德音。以警聋瞽之一二。则其所补益。何必相面而后足耶。答李景粹
昔年星山之学。猥随士友之后。得与足下讲讨一二。至于心性义理。无或相戾。有如同受旨诀于吾先生者。此何以哉。栎翁之于先生。其道义交契。彷佛乎尤翁之于同春。则其门人子弟。虽未得种种对讨。而其情谊流通。一见可以平生。宜足下先赐手墨。以道其惓惓也。彼一边人之诬陷渼门者。抑亦何心哉。鼎焕杜门以还。只可随分自守。而固陋涔寂。不堪其无聊。幸赖诸君子不鄙。时赐书问。劝诱辄至。未尝不惕然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8H 页
 兴吁。思所以自新。而家务俗累。种种缚人。使不得回转一步。则恐终为师友之羞也。足下夙就大方。中道梁摧。徊徨斯世。必不无安仿之叹也。昔春翁门人有若寒水先生者。亦尝问学于华阳之门。此有故事。以足下卓荦之姿。行古人博学之义。相与服勤于渼上之门。则抑吾前所道同受旨诀者。竟非虚语也。不审足下以为如何。仲烈新筑竹溪。可想其专于为学。尤使人深羡。况足下密迩其居。必有相观而善者乎。历访之教。非敢不勉。而顾有面前事。末由即遂。若丈席又或过冬于稽山。则春将贳马。以候起居于行窝。而兼欲历叩于意中之友。未前为道自重。以慰瞻仰。
兴吁。思所以自新。而家务俗累。种种缚人。使不得回转一步。则恐终为师友之羞也。足下夙就大方。中道梁摧。徊徨斯世。必不无安仿之叹也。昔春翁门人有若寒水先生者。亦尝问学于华阳之门。此有故事。以足下卓荦之姿。行古人博学之义。相与服勤于渼上之门。则抑吾前所道同受旨诀者。竟非虚语也。不审足下以为如何。仲烈新筑竹溪。可想其专于为学。尤使人深羡。况足下密迩其居。必有相观而善者乎。历访之教。非敢不勉。而顾有面前事。末由即遂。若丈席又或过冬于稽山。则春将贳马。以候起居于行窝。而兼欲历叩于意中之友。未前为道自重。以慰瞻仰。与金和仲(履鼎)
广寒楼月。秋来正明。无由坐我其上。与左右同其赏。则只喜有此月之分照我两人心也。子其幸相思否。仲春稽馆之别。其所赠言。只欲子之能于为学。而又使渐进于文章也。别后已阅炎凉。游泳发舒之馀。果有文学两进之效耶。古人之游江山楼观。消融其查滓。荡涤其心胸。虽无管弦丝竹之响。而能知山水之自有清音。则悠然景与意会。其一开口吐出胸中之奇。斐然有成章。子之游观。能有髣髴乎是也否。愚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8L 页
 之所望于子。岂徒玩物之乐而止也。其俯仰动止之间。能超然于物累之表。使天理流行而人欲净尽。则其发于文辞者。有足以灿然而可观矣。何患其无所学也。若独爱于物。而非学之为。则愚何敢复言耶。有相斋记。不揆文拙。率尔呈献。可发千里一笑耳。
之所望于子。岂徒玩物之乐而止也。其俯仰动止之间。能超然于物累之表。使天理流行而人欲净尽。则其发于文辞者。有足以灿然而可观矣。何患其无所学也。若独爱于物。而非学之为。则愚何敢复言耶。有相斋记。不揆文拙。率尔呈献。可发千里一笑耳。与金清道(履裕)
书面之相阻。居然三十年前事。屡次会行京里。旧要或相寻访。而至于尊兄。以其历宰于外。不得遂一会。此心耿怅。何尝少弛。曾因李明叟胤子。槩闻尊昆季责我以不一相访。吁其不忘矣。先伯氏虽以名宰见称。区区所执。则寒士之出入相门。盖有所不敢也。虽然吾辈之所相勉。不在于面与不面。惟以学不进为忧。而顾此孤陋。年近七耋。学无所成。时与士友往复难疑。稍有相长之益。而程先生所谓转令人薄者。不虚语也。岭中同门。举皆沦落。只馀郑仲烈及不佞在。向与仲烈对相讨论。大要不谋而同归。尤可喜也。尊兄以吾先君甲午所遭。想必嗟惜。而 英庙朝特蒙伸雪。台言落空。其时出于朝纸者。昭晰无馀。尊兄密迩 天陛。趁当获览 宣批。必以我为幸也。向之责我以不相访者。抑有是伸诬故耶。或出于故旧无大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9H 页
 故则不绝之义耶。其为鸣感则深耳。即闻尊兄来莅清道。此距仙衙。不过数宿程。岂不欲褰裳往讨。而年称辛酉者。衰谢转甚。谚所道同甲出宰。真尊兄谓也。千里从官。可想其神旺。而为尊兄供贺者。晚年邑号。皆从公清二字中出来。果以公清为政。则真不坠尊兄家法。而益张吾军矣。谨以一绝勉之曰。至公求道不违天。寡欲清神便是仙。若见大原无少累。许君能得圣贤传。未审尊兄以为如何。
故则不绝之义耶。其为鸣感则深耳。即闻尊兄来莅清道。此距仙衙。不过数宿程。岂不欲褰裳往讨。而年称辛酉者。衰谢转甚。谚所道同甲出宰。真尊兄谓也。千里从官。可想其神旺。而为尊兄供贺者。晚年邑号。皆从公清二字中出来。果以公清为政。则真不坠尊兄家法。而益张吾军矣。谨以一绝勉之曰。至公求道不违天。寡欲清神便是仙。若见大原无少累。许君能得圣贤传。未审尊兄以为如何。与韩重文
古人云树诗。徒相思也。而此则反之矣。时登武夷绝顶。望云山岧峣。髣髴乎足下气象。而恨不可亲也。不审起居稽馆。周旋丈席。随其动静语默。日有人不知而独觉其进之效否。尤不胜遥贺。鼎焕老人气力幸免甚损。间与村秀。略干讲论书史。亦足以随分而安也。足下近读甚书。其为学次第。则先生在。可想其不差。而顾交游之乐。固天下胜事。然乐非由学而得。则其乐也流。与不亦乐乎之乐异焉。敢不与足下相勉也。前春告别师门。语及足下。猥以此仰对而归。不知足下以为如何。南尚宽之凶书。实关世道。渠以幺么贱生。敢议到于师门。少无忌惮底意。亦可谓斯文之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19L 页
 贼。回顾今世。迄无齐声而共讨者。士气之萧索。一何至此。良可慨也。何幸足下恒侍函席。湖中动静。想皆经历。为此传致如何。士达仲茂。一与之相守否。别来亦相恋恋。士达夙许稗稿之评。而归甚匆匆。未闻其明批。是可纡郁也。早晚相见。幸以是告焉。景曾,坦叟近又来学耶。湖岭落落。彼此无由窥寻其声光。还不若始不相识之为愈也。所欲言非止于此。而明春似可更续旧游。姑略之耳。
贼。回顾今世。迄无齐声而共讨者。士气之萧索。一何至此。良可慨也。何幸足下恒侍函席。湖中动静。想皆经历。为此传致如何。士达仲茂。一与之相守否。别来亦相恋恋。士达夙许稗稿之评。而归甚匆匆。未闻其明批。是可纡郁也。早晚相见。幸以是告焉。景曾,坦叟近又来学耶。湖岭落落。彼此无由窥寻其声光。还不若始不相识之为愈也。所欲言非止于此。而明春似可更续旧游。姑略之耳。与金士达(相进)
讲说窒碍。每与诸友。未当不掩卷相恋也。重文谓有室忧。忽此告归。旅馆益寥落。安得起吾友来。周旋三席之间。与之共此学耶。向登落花台。怀想仁风。诗意颇怊然。韩友袖轴而往。早晚关照。庶有以谅此怀也。惟愿力学保重。以慰远望。
与金仁瑞
来谕谓有南觐时。与稽山朋友。相须甚勤。旋以事牵。失此团会。一瞻颜色。顾有数存焉耶。即此秋炎。先生气候。幸无甚损否。谓尝早晚还山。而虑有疠氛未霁。庸此趑趄。近或行次于云楼。而兄亦安侍读书否。抑归觐果可如教。而尚此陪游于二水官中否。华阳山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0H 页
 长事。先生处义。本不欲出。而至有敦请之举。则似不忍终拒。未知究竟何如也。向来世道不古。种种有宋魋怪举。安保无此辈肆然又作孽于其间耶。僻居穷乡。无由闻湖中近槩。幸可为此示及其详耶。吾辈处事一之地。便同子侄。凡此横逆之来。直而不报。亦一道也耶。每与明叟,南为。言之如此。未知盛筹云何。黄江权丈远摈绝海。亦关世运。未尝不掩卷而太息耳。
长事。先生处义。本不欲出。而至有敦请之举。则似不忍终拒。未知究竟何如也。向来世道不古。种种有宋魋怪举。安保无此辈肆然又作孽于其间耶。僻居穷乡。无由闻湖中近槩。幸可为此示及其详耶。吾辈处事一之地。便同子侄。凡此横逆之来。直而不报。亦一道也耶。每与明叟,南为。言之如此。未知盛筹云何。黄江权丈远摈绝海。亦关世运。未尝不掩卷而太息耳。与南汉朝
弱冠邂逅。倏已四十馀载。中间忧戚。几于相忘。尽东人诗话所道北海南溟限门闾也。时因甥儿来往。为问起居动静。而早谢公车。专心此学。是好消息也。居今之世。谈古之道。虽似迂远。而心胆相照。则吴越便是衽席。此何以哉。闻老兄晚来。心性等论。大略与洛学相似者。岂非不期而然哉。是以不揆孤陋。敢以所闻于师友者。为老兄略陈之。大率从古论性。只有二途。本然气质而已。就气质中。除却气单指其理。谓之本然。以理与气质杂而言之。谓之气质。朱夫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者。非不言气。而所主在于理。中庸天命之性是也。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非不言理。而所主在于气。孟子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0L 页
 犬牛人之性是也。故朱子又曰中庸天命之性。是通天下一性。而至论犬牛人之性。直断之为气质之性。其意可知也。湖中一种议论。以中庸首章。谓兼气质。而人物性各不同。又以孟子犬牛人章。谓单指本然之性。若是则果与朱子之说。合乎否乎。或人之跋寒泉诗后曰。泉门凡言人性之异于禽兽者。皆以为气质而非本然。则是不知人兽之别。而陷于释氏之见云。果如是则其亦异乎程朱之说矣。明道先生曰万物一体。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释氏以不知此。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朱子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不杂气禀而言。是专言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又曰万物皆只同这一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推是观之则其谓本性之不同者是乎。其归以释氏之见者果然乎。或人曰二十二章三性字。皆以本性言。若指气质之性则气质之性亦可尽者乎。人物之性果同。而圣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则岂可谓尽物之性乎。(此在南塘记闻录中。)此恐不通之论也。物性虽不同于人。亦各
犬牛人之性是也。故朱子又曰中庸天命之性。是通天下一性。而至论犬牛人之性。直断之为气质之性。其意可知也。湖中一种议论。以中庸首章。谓兼气质。而人物性各不同。又以孟子犬牛人章。谓单指本然之性。若是则果与朱子之说。合乎否乎。或人之跋寒泉诗后曰。泉门凡言人性之异于禽兽者。皆以为气质而非本然。则是不知人兽之别。而陷于释氏之见云。果如是则其亦异乎程朱之说矣。明道先生曰万物一体。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释氏以不知此。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朱子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不杂气禀而言。是专言理。若云兼言气。便说率性之道不去。又曰万物皆只同这一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推是观之则其谓本性之不同者是乎。其归以释氏之见者果然乎。或人曰二十二章三性字。皆以本性言。若指气质之性则气质之性亦可尽者乎。人物之性果同。而圣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则岂可谓尽物之性乎。(此在南塘记闻录中。)此恐不通之论也。物性虽不同于人。亦各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1H 页
 有本然可尽之道。故圣人随其不同之分。而因其可尽之道。处之无不当。即所以尽其性也。使马之悍者而可驾之。牛之触者而可犁之。又使鸟兽鱼鳖咸若之类是也。彼所谓圣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者。亦不善辨者也。万物之形质既异。则虽欲做人底事而末之难矣。何独物也。下愚之不移。圣人付之于自㬥。则名虽为人而与禽兽奚择哉。中庸首章统言人物所同得之本性。则岂非朱子所谓不杂气禀而言者耶。盖中庸一部。无论首章与二十二章。皆言理同而气异。则前所道非不言气而所主在于理者此也。彼每以理同气异为言。而不曰性同气异者。抑又何哉。朱子答徐元聘书性同气异四字。已是八字打开。苟于此四字。看得分明。则其于论性论气。或离或合。皆沛然无疑矣。未知老兄以为如何。又有一学者望士也。尝为明德图。以黑暗画圈子。就黑中为一小白圈子。分书清浊粹驳虚灵不昧等字曰。圣凡贤愚。明德有分数。虚灵有优劣。愚驳之曰未知众人方寸。若是黑暗。终无变化气质之时。而与禽兽之不能变化者。一体同归也哉。愚之所为明德图。圣凡通为一图。而但气质自有不齐之分。及其变化气质。则凡人之明德
有本然可尽之道。故圣人随其不同之分。而因其可尽之道。处之无不当。即所以尽其性也。使马之悍者而可驾之。牛之触者而可犁之。又使鸟兽鱼鳖咸若之类是也。彼所谓圣人不能使物做人底事者。亦不善辨者也。万物之形质既异。则虽欲做人底事而末之难矣。何独物也。下愚之不移。圣人付之于自㬥。则名虽为人而与禽兽奚择哉。中庸首章统言人物所同得之本性。则岂非朱子所谓不杂气禀而言者耶。盖中庸一部。无论首章与二十二章。皆言理同而气异。则前所道非不言气而所主在于理者此也。彼每以理同气异为言。而不曰性同气异者。抑又何哉。朱子答徐元聘书性同气异四字。已是八字打开。苟于此四字。看得分明。则其于论性论气。或离或合。皆沛然无疑矣。未知老兄以为如何。又有一学者望士也。尝为明德图。以黑暗画圈子。就黑中为一小白圈子。分书清浊粹驳虚灵不昧等字曰。圣凡贤愚。明德有分数。虚灵有优劣。愚驳之曰未知众人方寸。若是黑暗。终无变化气质之时。而与禽兽之不能变化者。一体同归也哉。愚之所为明德图。圣凡通为一图。而但气质自有不齐之分。及其变化气质。则凡人之明德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1L 页
 可化为圣贤。到此之时。岂有分数之一定而优劣之可论哉。彼终不为然。付之于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耳。凡看义理文字。大著公眼目然后。于甲于乙。庶免牵合先入之惑矣。老兄必有素讲于平日者。玆仰质焉。南中先辈文集孤陋未多览焉。大率此等议论。在于西人集中。而近来湖洛之论。又从以纷起。甲曰吾从朱子。乙曰吾从朱子。便同以朱子攻朱子。盖缘于朱子之论。初晚之不同故也。所欲质者。不止于此。而儿行急遽。当俟后日矣。老兄案上。必有劄录。如有可论者。幸须投示也。
可化为圣贤。到此之时。岂有分数之一定而优劣之可论哉。彼终不为然。付之于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耳。凡看义理文字。大著公眼目然后。于甲于乙。庶免牵合先入之惑矣。老兄必有素讲于平日者。玆仰质焉。南中先辈文集孤陋未多览焉。大率此等议论。在于西人集中。而近来湖洛之论。又从以纷起。甲曰吾从朱子。乙曰吾从朱子。便同以朱子攻朱子。盖缘于朱子之论。初晚之不同故也。所欲质者。不止于此。而儿行急遽。当俟后日矣。老兄案上。必有劄录。如有可论者。幸须投示也。答李▣▣(宗汉)
去年春。远赐垂问。兼有诗什之贶。一读一咏。欣豁不可量。而愧无以即报也。伏惟冬令乖侯。静候神相万吉。仰溯区区。鼎焕老人气力粗保。幸无以为谕也。向闻执事有平海之 命。平海薄邑也。禄不足以仁其三族。而执事政化之未尽施于武陵者。谓可以小宣于此矣。上府未察。使执事之贤。犹未免中途而递。天下有不可知之事也。何叹如之。
答李明叟
聚日有期。属与山妻谋酿已熟。此际书至人不至。吾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2H 页
 饮而酬之者谁欤。讲而讨之者谁欤。自恨平日不见信于朋友。而甚至于欺我家人如此。宜其引壶独酌。以代古人自罚之义也。伏惟色忧快霁。学履佳胜。区区欣慰。何可量也。丈席金陵之报。远无以及闻。此去金山二百里。恨不致身于师友之侧。与闻其绪馀耳。沈李诸人之就学。岂不欣悦。而金斯文之归正。又何奇也。非力量之大识理之明。其何以办此。嗟乎。环岭七十州。一变至道。有如此人。则比屋之美。又何可量也耶。鼎焕老人气力。遇寒辄损。此非远游之日。而及吾丈席未撤。随诸友之后。以了生平未尽之债。固愿也。而顾有面前些事。此若了当。似过今月念日。恐难为此等待。兄其行矣。
饮而酬之者谁欤。讲而讨之者谁欤。自恨平日不见信于朋友。而甚至于欺我家人如此。宜其引壶独酌。以代古人自罚之义也。伏惟色忧快霁。学履佳胜。区区欣慰。何可量也。丈席金陵之报。远无以及闻。此去金山二百里。恨不致身于师友之侧。与闻其绪馀耳。沈李诸人之就学。岂不欣悦。而金斯文之归正。又何奇也。非力量之大识理之明。其何以办此。嗟乎。环岭七十州。一变至道。有如此人。则比屋之美。又何可量也耶。鼎焕老人气力。遇寒辄损。此非远游之日。而及吾丈席未撤。随诸友之后。以了生平未尽之债。固愿也。而顾有面前些事。此若了当。似过今月念日。恐难为此等待。兄其行矣。答李明叟
庭树荫绿。蝉声益清。未尝不怀仰高风。忽此新溪使至。获承兄前后惠书。其为披豁。无异东坡咏宝月而蹶起也。信后日久。行旆无挠。学履佳吉。瞻溯区区。鼎焕奉亲粗遣。而目倦心昏。未能专意看书。且日用功夫。亦未见合了义理。几何不为朋友弃也。大率吾辈各处远地。只有书牍一路。仍此讲其所闻质其所疑。无相忘渼上别时语幸也。且有至愿。谢绝尘埃。结屋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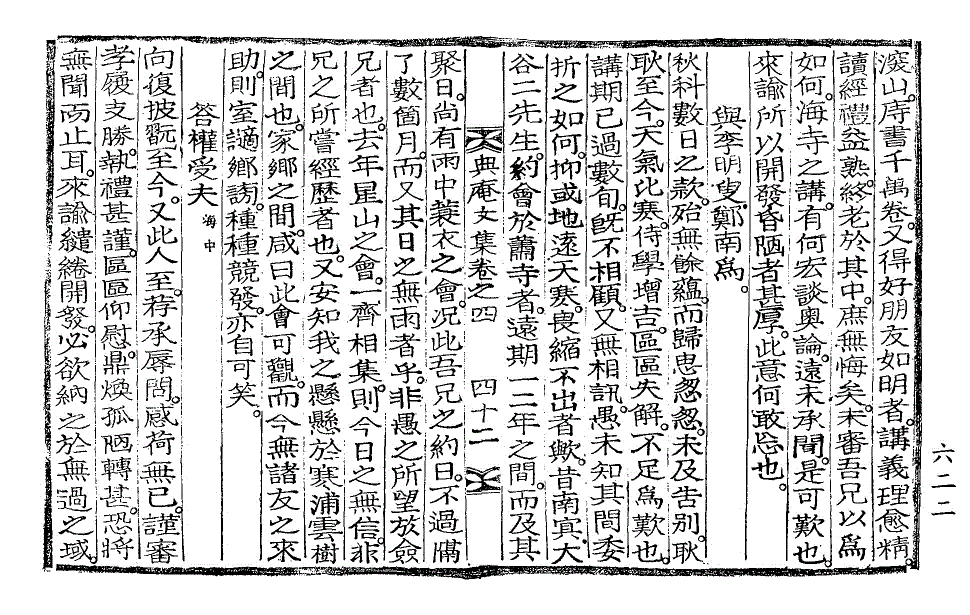 深山。庤书千万卷。又得好朋友如明者。讲义理愈精。读经礼益熟。终老于其中。庶无悔矣。未审吾兄以为如何。海寺之讲。有何宏谈奥论。远未承闻。是可叹也。来谕所以开发昏陋者甚厚。此意何敢忘也。
深山。庤书千万卷。又得好朋友如明者。讲义理愈精。读经礼益熟。终老于其中。庶无悔矣。未审吾兄以为如何。海寺之讲。有何宏谈奥论。远未承闻。是可叹也。来谕所以开发昏陋者甚厚。此意何敢忘也。与李明叟,郑南为。
秋科数日之款。殆无馀蕴。而归思匆匆。未及告别。耿耿至今。天气比寒。侍学增吉。区区失解。不足为叹也。讲期已过数旬。既不相顾。又无相讯。愚未知其间委折之如何。抑或地远天寒。畏缩不出者欤。昔南冥,大谷二先生。约会于萧寺者。远期一二年之间。而及其聚日。尚有雨中蓑衣之会。况此吾兄之约日。不过隔了数个月。而又其日之无雨者乎。非愚之所望于佥兄者也。去年星山之会。一齐相集。则今日之无信。非兄之所尝经历者也。又安知我之悬悬于寒浦云树之间也。家乡之间。咸曰此会可观。而今无诸友之来助。则室谪乡谤。种种竞发。亦自可笑。
答权受夫(海中)
向复披玩至今。又此人至。荐承辱问。感荷无已。谨审孝履支胜。执礼甚谨。区区仰慰。鼎焕孤陋转甚。恐将无闻而止耳。来谕缱绻开发。必欲纳之于无过之域。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3H 页
 甚矣哀兄之爱我也。谨当思所未至。勉所未及。庶副期望之万一耳。明叟近过高轩。得一宿之款。所论想益精密。远未闻一二可恨也。承有鲁论之课。其手舞足蹈。果如程先生说也否。虽然居忧读礼。自是一事。愚闻之丧礼一依朱文公家礼。若有窒碍处。参之以击蒙要诀。勿为苟且从俗。且衰绖非疾病服役不敢脱。此语甚好。又不可不知也。
甚矣哀兄之爱我也。谨当思所未至。勉所未及。庶副期望之万一耳。明叟近过高轩。得一宿之款。所论想益精密。远未闻一二可恨也。承有鲁论之课。其手舞足蹈。果如程先生说也否。虽然居忧读礼。自是一事。愚闻之丧礼一依朱文公家礼。若有窒碍处。参之以击蒙要诀。勿为苟且从俗。且衰绖非疾病服役不敢脱。此语甚好。又不可不知也。与俞擎汝(崧柱○辛卯)
鼎焕索居固陋。旧学愈荒。窃以师友之远。为夙夕之忧。乃者先生就养稽山。途比渼江。几减半千馀里。而行之不力。犹未得朝夕就正之乐。中间猥随诸友之后。纳拜师席。仍受近思数篇。上下讨论。自以谓粗有分寸之进。及退居穷乡。家务俗累。种种缚人。回转不得。则放失者多。存在者小。荏苒颓倒。犬马之齿。今三十有一矣。读书观理。未有可望之效。中夜以思。怛然内疚。吾兄将何以教之。向风引领。不任驰情。伏惟侍学增吉。宿患快祛。区区朋友之望。尤无以名喻也。自古英豪之士。虽未有因学致疾。而偶或有先病而后瘳者。非针药所能及。正须致养其丹田气海。则天君泰然。四支百体。利于从令矣。大抵吾兄之病。或其一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3L 页
 蹴可到于圣贤之学。而有以自致也。呜呼。此何易也。儒者之学。最贵于循序而渐进。亦莫切于平心而易气。使吾方寸之灵。惺惺不已。无昏昧之失。纷起之扰。然后为至。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长。以至枝叶华实。不待其日至之时。而揠焉以助之长。岂不无益而反害之哉。荷相与之勤。敢布腹心如此。兄其恕纳焉。向来湖通之变。实关世道。此可谓横逆之来。何损于吾先生之盛德哉。自一善有答通之举。且吾南士君子之执贽于师门者甚众。亦足以张吾军也。
蹴可到于圣贤之学。而有以自致也。呜呼。此何易也。儒者之学。最贵于循序而渐进。亦莫切于平心而易气。使吾方寸之灵。惺惺不已。无昏昧之失。纷起之扰。然后为至。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长。以至枝叶华实。不待其日至之时。而揠焉以助之长。岂不无益而反害之哉。荷相与之勤。敢布腹心如此。兄其恕纳焉。向来湖通之变。实关世道。此可谓横逆之来。何损于吾先生之盛德哉。自一善有答通之举。且吾南士君子之执贽于师门者甚众。亦足以张吾军也。与李士宗
曩在稽山。从容丈席。饫承德诲。退与二三诸友。上下讨论。恍如时斋旧游。而只恨座上无吾士宗昆季。与之共此乐。且吾兄诗人也。往往相恋于良辰暇日。陶写性情。而又无以慰此怀。则未尝不披诸箧诗。三复而太息也。今年科事。岭之同门中。李明叟,郑南为以其文章大手。皆未免落莫矣。未知吾兄得失何居。得则甚喜。而失亦不足为叹。世以学问为一大事。不可几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于科举之文。乃欲以为父母之荣。门户之计者。皆末失也。吾兄于此。讲之素明。而犹未免应举之似急于为学。玆切所未谕也。敢忘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4H 页
 其僭踰。仰陈至此。兄其徐究耶。悚仄悚仄。石院讲会。一向济济否。俞擎汝旧疾快祛。朋友之幸大矣。先生之就养稽山。在岭友可谓得矣。而如兄穷儒。想难远游。为之深叹。岭中与永同近。兄其讲学之暇。告于函席。而与李郑诸人。联袂南游。上伽倻绝顶。访崔孤云陈迹。亦世间一快也。幸另图焉。
其僭踰。仰陈至此。兄其徐究耶。悚仄悚仄。石院讲会。一向济济否。俞擎汝旧疾快祛。朋友之幸大矣。先生之就养稽山。在岭友可谓得矣。而如兄穷儒。想难远游。为之深叹。岭中与永同近。兄其讲学之暇。告于函席。而与李郑诸人。联袂南游。上伽倻绝顶。访崔孤云陈迹。亦世间一快也。幸另图焉。与李善长(廷仁)
去冬仍稽山官递。率尔献复书。计获关照也。信后忽已经年。伏惟茂纳新休。德学俱进。尤不胜遥贺。鼎焕奉亲粗遣。而回顾平生。了无所成。居然为三十一齿人。如是悠悠。恐将无闻而止耳。示喻礼意甚勤。而所以教诲责望者重。非相爱之深。何以及此。自顾固陋。非敢经事于礼学。而僻居穷乡。至如冠昏丧祭之仪。非有所讲于平閒之时。易失于急遽之际。是甚可惧。所以在渼上抄礼疑数条。禀告于先生。先生仍手书颜子四勿之目。曾子三贵之戒而赐之。其不鄙之教。于是益切矣。行之不力。旧习常仍。种种闯发于朋友讨论之际。以致吾兄今日之戒也。敢不勉其所不足也。承有程门之课。主敬穷理。而日用之间。且有以得乎先生之心。果如朱夫子序说否。时斋重修事。来教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4L 页
 甚善。而大抵此斋规模狭隘。甚非大庇之意也。仁瑞之主张。吾兄之首论。出于商量。而诸友以丈席之来次稽山。皆欲观后以为计。不可一二说谕而办了。异日渼上之会。当公议相确。以完是事。亦非晚也。未知吾兄以为如何。顷因便风。闻有再醮之仪。仍此可想其室家之乐。而又得无门外徵租之虞否。吾辈穷儒。未尝不动心于此。然贫者士之常。惟无易其所操则甚善。吾兄想折肱于斯。何待相勉而后知也。
甚善。而大抵此斋规模狭隘。甚非大庇之意也。仁瑞之主张。吾兄之首论。出于商量。而诸友以丈席之来次稽山。皆欲观后以为计。不可一二说谕而办了。异日渼上之会。当公议相确。以完是事。亦非晚也。未知吾兄以为如何。顷因便风。闻有再醮之仪。仍此可想其室家之乐。而又得无门外徵租之虞否。吾辈穷儒。未尝不动心于此。然贫者士之常。惟无易其所操则甚善。吾兄想折肱于斯。何待相勉而后知也。与李善长
伏惟献岁发春。静中经履茂膺川嘏。且日用之间。动静之际。有蝉蜕春融之妙耶。尤不胜遥贺。鼎焕落拓还乡。担阁功令之业。专治旧学。虽有孤陋之叹。而亦不无自得之效。不知日之将夕。老之将至。益觉吾道中。自有乐地矣。冬间以宗侄丧葬之扰。日事悲遑。今则已归于安閒境界。又是读书人也。近读孟子犬牛人章。知三性之不同。皆气质故也。朱子曰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因是推之则朱子章句所谓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此言气犹相近。)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言理绝不同。)盖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知气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5H 页
 犹相近。)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不知理绝不同。)是故尤翁手录杂著曰。孟子犬牛人之性。气质也。岂非朱子所谓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岂徒此章之旨为然。论语性相近章小注曰天命之谓性。则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气质而言。孟子犬牛人之殊。亦指此而言。南塘跋寒泉诗后云凡言人性之异于禽兽者。皆以为气质而非本然。则是不知人兽之别。陷于释氏之见。若尔则尤翁亦不免其责。而朱子章句之释。皆归空阙语耶。且夫西山真氏亦有中庸则理同而气异。(大学亦然。)孟子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在中庸首章小注。)与朱夫子之说。了无异同矣。崔叔固往于南塘。面质之曰门下以谓中庸天命之性。人物不同乎。曰然。曰有所据否。曰孟子犬牛人章。明白丁宁。而栗翁曰人之性。非物之性。又曰性不能禀全德。尤翁曰物不具五常。以此知之云。愚不觉掩卷而太息也。栗尤两先生之训。皆释犬牛人理绝不同处也。以理不同者而观之。则人之性。非物之性也。性不能禀全德。而物不具五常也。南塘奈何以犬牛人理不同者。释之于天命之性理同处耶。中庸理同也。故朱子章句释之曰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犹相近。)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不知理绝不同。)是故尤翁手录杂著曰。孟子犬牛人之性。气质也。岂非朱子所谓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岂徒此章之旨为然。论语性相近章小注曰天命之谓性。则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气质而言。孟子犬牛人之殊。亦指此而言。南塘跋寒泉诗后云凡言人性之异于禽兽者。皆以为气质而非本然。则是不知人兽之别。陷于释氏之见。若尔则尤翁亦不免其责。而朱子章句之释。皆归空阙语耶。且夫西山真氏亦有中庸则理同而气异。(大学亦然。)孟子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此在中庸首章小注。)与朱夫子之说。了无异同矣。崔叔固往于南塘。面质之曰门下以谓中庸天命之性。人物不同乎。曰然。曰有所据否。曰孟子犬牛人章。明白丁宁。而栗翁曰人之性。非物之性。又曰性不能禀全德。尤翁曰物不具五常。以此知之云。愚不觉掩卷而太息也。栗尤两先生之训。皆释犬牛人理绝不同处也。以理不同者而观之。则人之性。非物之性也。性不能禀全德。而物不具五常也。南塘奈何以犬牛人理不同者。释之于天命之性理同处耶。中庸理同也。故朱子章句释之曰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5L 页
 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岂非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者耶。其下又释之曰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此岂非气异者耶。叔固不以此辨。而只据中庸二十章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则理同而气异也。乌可引是以为孟子犬牛人三性不同之證也耶。三性之不同。乃所谓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如是云云。宜其不能屈南塘也。尝观巍岩寒泉之论。皆不以理绝不同为言。而只以气质为辨者。不免费辞说。尝闻之师。天命之性。人与物一同。而今恨无处就正也。兄则其有所异之闻否。幸示之也。愚之所论。虽质之于先师。不以愚为非也。未知兄意如何。大抵南塘非不知一原之时。人物性之皆同。而其误入处。以异体看本然也。既是异体则气犹相近于二五之杂。而合下一原之理则绝不同也。天命之性。非别有一性。乃一原理同之性也。岂有人物不同之理哉。及其异体之后。虑其有后人之认气为性也。故朱夫子答人书。辄曰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其下又云不可谓无是性。推是以论则一原之初。均得是性者。盖可见矣。噫南塘岂不知此等经义。而与泉门各立。驱一世于雄辩之囿。出此一种新奇之谈。
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岂非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者耶。其下又释之曰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此岂非气异者耶。叔固不以此辨。而只据中庸二十章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则理同而气异也。乌可引是以为孟子犬牛人三性不同之證也耶。三性之不同。乃所谓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如是云云。宜其不能屈南塘也。尝观巍岩寒泉之论。皆不以理绝不同为言。而只以气质为辨者。不免费辞说。尝闻之师。天命之性。人与物一同。而今恨无处就正也。兄则其有所异之闻否。幸示之也。愚之所论。虽质之于先师。不以愚为非也。未知兄意如何。大抵南塘非不知一原之时。人物性之皆同。而其误入处。以异体看本然也。既是异体则气犹相近于二五之杂。而合下一原之理则绝不同也。天命之性。非别有一性。乃一原理同之性也。岂有人物不同之理哉。及其异体之后。虑其有后人之认气为性也。故朱夫子答人书。辄曰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其下又云不可谓无是性。推是以论则一原之初。均得是性者。盖可见矣。噫南塘岂不知此等经义。而与泉门各立。驱一世于雄辩之囿。出此一种新奇之谈。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6H 页
 又见叔固所录尤翁说犬牛人不同之性。皆气质而非本然。则尤翁即栗翁之的传也。刱闻尤翁之有是说。而不觉辞穷胆寒。于是下一转语曰尤翁之意。以为孟子虽不言气质。其言犬牛人不同处。亦以气质言。盖以追补未备之意。非谓犬牛人之性。皆非本然也。其为言也。要立己见。而反露自家之情状也。凡言本然之性。则犬牛人皆同。言气质之性则犬牛人又不同。若以本然之性谓一原。则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而以其所谓本然者。就诸异体而言。则这便是认气为性者。其可乎哉。异体之上。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则人物之性所以异者。气质而已。本然二字。非所与论也。南塘之意。又以谓一原则本然至善。而异体本然则善恶相混也。故释本然之义曰人之正且通者。天所以本自如是。物之偏且塞者。天又所以本自如是。若使南塘反躬自省。以本然者归之于一原。而曰人物之性皆同。以气质者归之于异体。而曰人物之性不同云尔。则岂非亭当者乎。由前之答崔成仲书。则人物之性。同与不同。在理气之间。由后之答崔叔固言。则人物之性不同。在于天命之性。此非两截之论而何也。惜乎不善变也。所欲言者多。而纸尽止此。
又见叔固所录尤翁说犬牛人不同之性。皆气质而非本然。则尤翁即栗翁之的传也。刱闻尤翁之有是说。而不觉辞穷胆寒。于是下一转语曰尤翁之意。以为孟子虽不言气质。其言犬牛人不同处。亦以气质言。盖以追补未备之意。非谓犬牛人之性。皆非本然也。其为言也。要立己见。而反露自家之情状也。凡言本然之性。则犬牛人皆同。言气质之性则犬牛人又不同。若以本然之性谓一原。则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而以其所谓本然者。就诸异体而言。则这便是认气为性者。其可乎哉。异体之上。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则人物之性所以异者。气质而已。本然二字。非所与论也。南塘之意。又以谓一原则本然至善。而异体本然则善恶相混也。故释本然之义曰人之正且通者。天所以本自如是。物之偏且塞者。天又所以本自如是。若使南塘反躬自省。以本然者归之于一原。而曰人物之性皆同。以气质者归之于异体。而曰人物之性不同云尔。则岂非亭当者乎。由前之答崔成仲书。则人物之性。同与不同。在理气之间。由后之答崔叔固言。则人物之性不同。在于天命之性。此非两截之论而何也。惜乎不善变也。所欲言者多。而纸尽止此。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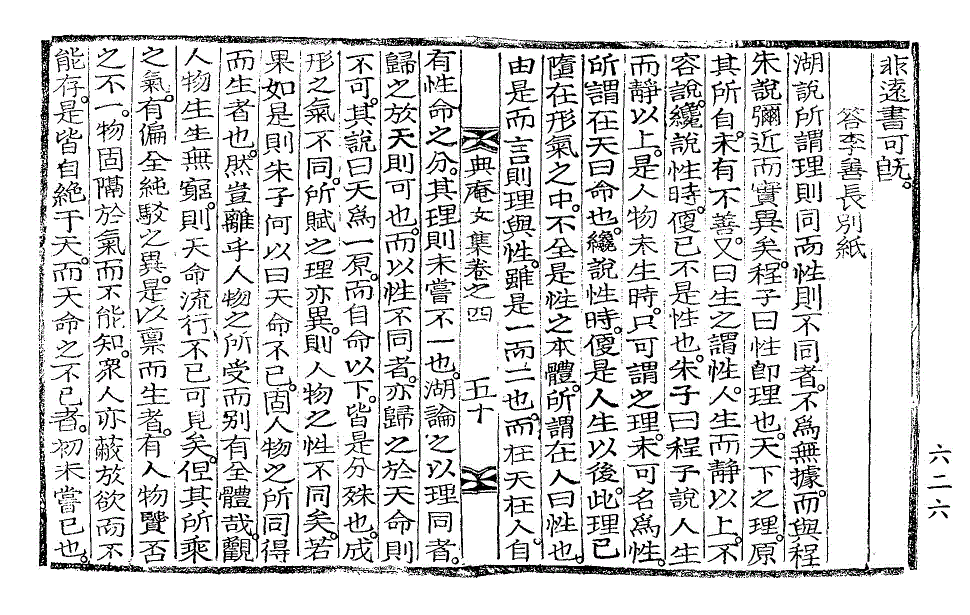 非远书可既。
非远书可既。答李善长别纸
湖说所谓理则同而性则不同者。不为无据。而与程朱说弥近而实异矣。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程子说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所谓在人曰性也。由是而言则理与性。虽是一而二也。而在天在人。自有性命之分。其理则未尝不一也。湖论之以理同者。归之于天则可也。而以性不同者。亦归之于天命则不可。其说曰天为一原。而自命以下。皆是分殊也。成形之气不同。所赋之理亦异。则人物之性不同矣。若果如是则朱子何以曰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而生者也。然岂离乎人物之所受而别有全体哉。观人物生生无穷。则天命流行不已可见矣。但其所乘之气。有偏全纯驳之异。是以禀而生者。有人物贤否之不一。物固隔于气而不能知。众人亦蔽于欲而不能存。是皆自绝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未尝已也。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7H 页
 湖论之引而为證者。徒知理同者天为一原。而不知性不同者。由于气质而非天之一原也。或问于朱子曰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理之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万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而生者言之。理则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朱子曰然。然则湖说所谓天为一原。性为分殊。性为一原而道为分殊者。殊涉破碎。以其天为一原者而论之则人物无贵贱之殊。以其性为一原者而观之则人物得全体之理。岂有分殊之可言耶。就其气禀之中。各有偏全粹驳之异。则朱子所谓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此其所谓分殊者也。而未闻一原之有分殊矣。又湖论以天命性分作三层看。言天于阴阳五行之先。言命于成形理赋之下。言性于人物各得之后者。其意不过以天为太极之一原。而自命以下。为分殊者也。又言成形之气不同。所赋之理亦异。则人物之性不同矣。又命为一原。性为分殊。盖自继善而言则命之流行一般。自成性而言则性之所受不同故也。其所为说。虽似巧妙。而以命为一原则自天所
湖论之引而为證者。徒知理同者天为一原。而不知性不同者。由于气质而非天之一原也。或问于朱子曰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理之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万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而生者言之。理则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朱子曰然。然则湖说所谓天为一原。性为分殊。性为一原而道为分殊者。殊涉破碎。以其天为一原者而论之则人物无贵贱之殊。以其性为一原者而观之则人物得全体之理。岂有分殊之可言耶。就其气禀之中。各有偏全粹驳之异。则朱子所谓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此其所谓分殊者也。而未闻一原之有分殊矣。又湖论以天命性分作三层看。言天于阴阳五行之先。言命于成形理赋之下。言性于人物各得之后者。其意不过以天为太极之一原。而自命以下。为分殊者也。又言成形之气不同。所赋之理亦异。则人物之性不同矣。又命为一原。性为分殊。盖自继善而言则命之流行一般。自成性而言则性之所受不同故也。其所为说。虽似巧妙。而以命为一原则自天所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7L 页
 赋予万物而言之。朱夫子所谓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则天以此理命于人者是也。以性为一原则继之者善也。性之流行一般。朱夫子所谓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则人以此性得于天者是也。由是而言则一原自一原也。岂可以分殊者当之耶。自成性而言之。则朱子曰天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然所谓气质者。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所谓气质之性者也。以分殊而言则人人不同。物物不同。然天命之不已则一而已。一者理也。若以三层看之。则天命为一层。性为一层。气质为一层。统而论之。在天在人。虽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则未尝不同。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一也。朱子所以答或问。而只曰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而已。则其所分殊者。在于气禀之不齐。而不在于天命之不已也。朱子又曰所谓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推此以求则性即理也之说。于是晓然矣。乌在其人物之性。不同于一原而有分殊者耶。
赋予万物而言之。朱夫子所谓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则天以此理命于人者是也。以性为一原则继之者善也。性之流行一般。朱夫子所谓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职。则人以此性得于天者是也。由是而言则一原自一原也。岂可以分殊者当之耶。自成性而言之。则朱子曰天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气与质也。人物得是气质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则谓之性。然所谓气质者。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所谓气质之性者也。以分殊而言则人人不同。物物不同。然天命之不已则一而已。一者理也。若以三层看之。则天命为一层。性为一层。气质为一层。统而论之。在天在人。虽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则未尝不同。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一也。朱子所以答或问。而只曰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而已。则其所分殊者。在于气禀之不齐。而不在于天命之不已也。朱子又曰所谓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推此以求则性即理也之说。于是晓然矣。乌在其人物之性。不同于一原而有分殊者耶。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8H 页
 答李善长别纸
答李善长别纸朱子曰天地之性。专指理而言。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性善。程子所谓极本穷原之性。张子所谓性者万物之一原。邵子所谓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是也。朱子又曰气质之性。以理杂气而言。张子所谓气质之性。告子所谓生之谓性。程子所谓生质之性。所禀之性。才出于气之性是也。自其天命之性言之。则性即理也。尧舜至于涂人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也。有善而无恶。天地之间。公共之理。而非有我之得私也。自其气质之性言之。则有偏正纯驳昏明厚薄之不齐。故性之在是者。其为品亦不一。人之性。非物之性也。有善而有恶。如水本至清。而土汩之则不能无浊也。合天命与气质而论性。则人物之性。同于一原者。天命之性也。分于异体者。气质之性也。然则人物之性。同与不同。可见于本然与气质也。湖论曰成形之气不同。所赋之理亦异。则人物之性不同矣。气以成形而后理方赋于其中。则性之与气质。又无时而可离。又曰人物所得之理不同。故性之所赋。物各不同。此便是认气质为本然也。天命之初。虽有气之清浊粹驳。而理自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8L 页
 理气自气。不相杂糅。其赋予万物。莫非全体之性也。及其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则不全是性之本体矣。见其人物之蔽于气汩于欲者。自绝于天命。而不知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也。则此何异于彪德远所谓天命惟人得之。而物无所与之论哉。朱夫子而复作则其驳湖说也。必不翅如彪说而已也。来书似欲洞究而不已。故不惮重溷及是。更加细商如何。顷贡图说。固出于妄作。而盛见颇以心性之置于太极圈内为不衬。此盖退溪李先生作天命图。圈之以太极而置心性之圈于其中。因为之说曰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则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朱子于太极图解。得其秀而最灵下。释之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所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又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由是而观则心字之置于圈中。不为无据矣。且夫人心之未发。即天地之心也。五常之性。即心中之理也。故朱子曰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盖其言心性。每每相随。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会之地也。愚是以于图
理气自气。不相杂糅。其赋予万物。莫非全体之性也。及其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则不全是性之本体矣。见其人物之蔽于气汩于欲者。自绝于天命。而不知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尝已也。则此何异于彪德远所谓天命惟人得之。而物无所与之论哉。朱夫子而复作则其驳湖说也。必不翅如彪说而已也。来书似欲洞究而不已。故不惮重溷及是。更加细商如何。顷贡图说。固出于妄作。而盛见颇以心性之置于太极圈内为不衬。此盖退溪李先生作天命图。圈之以太极而置心性之圈于其中。因为之说曰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则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朱子于太极图解。得其秀而最灵下。释之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所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又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由是而观则心字之置于圈中。不为无据矣。且夫人心之未发。即天地之心也。五常之性。即心中之理也。故朱子曰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盖其言心性。每每相随。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会之地也。愚是以于图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9H 页
 之上面。列书五性。就心篆中。又书性理字。然后可以见吻合之妙矣。至若真而静者未发也。动其中者已发之几。而发之者气也。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形既生矣。神发智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者。乃通书所谓几善恶也。虽在一圈之中。而性发为情则四端七情。又合为一圈者。盖取尤翁所谓发之之时。其气清明则理亦纯善。其气纷杂则理亦为所掩也。退溪作心统性情图。以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作一圈。以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又作一圈。栗谷驳之曰殊不知四端七情皆气发而理乘之。愚之所以合为一圈者。亦以此也。下圈中书两个心字者。非不知叠出。而既以程子说为图。则所谓觉者约其情。正其心养其性。使合于中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而求知焉。此其上心字。正其心之心字也。下心字。明诸心之心字也。便同退溪仁说图中。其许多仁字。从仁说而图之。则虽十个仁字。皆是一个仁字中出来者也。以此较彼。虽叠书心字。而势不得不然也。大抵图不尽意。自昔而然。幸不以图害意如何。
之上面。列书五性。就心篆中。又书性理字。然后可以见吻合之妙矣。至若真而静者未发也。动其中者已发之几。而发之者气也。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形既生矣。神发智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者。乃通书所谓几善恶也。虽在一圈之中。而性发为情则四端七情。又合为一圈者。盖取尤翁所谓发之之时。其气清明则理亦纯善。其气纷杂则理亦为所掩也。退溪作心统性情图。以四端为理发而气随之。作一圈。以七情为气发而理乘之。又作一圈。栗谷驳之曰殊不知四端七情皆气发而理乘之。愚之所以合为一圈者。亦以此也。下圈中书两个心字者。非不知叠出。而既以程子说为图。则所谓觉者约其情。正其心养其性。使合于中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而求知焉。此其上心字。正其心之心字也。下心字。明诸心之心字也。便同退溪仁说图中。其许多仁字。从仁说而图之。则虽十个仁字。皆是一个仁字中出来者也。以此较彼。虽叠书心字。而势不得不然也。大抵图不尽意。自昔而然。幸不以图害意如何。与尹使君(彝铉)
千里税驾。气候不瑕受损。向风瞻慕。不任憧憧。鼎焕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29L 页
 年踰七旬。何所求于斯世哉。至于讲学明道。惟以未死为期。然聪明顿铄。如盛漏器。随得随忘。如是而冀其髣髴耶。良可浩叹。先师文敬公。常景仰乎三学士先生。而至先先生忠贞公。尤致缱绻也。往年华宗衮金浦宰。以寒食祀官。见鄙先人于 章陵直中。谓鼎焕密迩渼上语。先人以清阴故事。因出忠贞古镜。相与摩挲久之。要获镜铭于渼翁。而往事已矣。故知府仁瑞氏。以渼翁之孙。而下车先访桐翁墓所在。就其下筑精舍。岁以重九荐菊。多士因推公为洞主。依鹿院故事。方立规听讲。而金公适以事还朝。幽明遽隔。至今乡士所共痛恨也。今明府以同义之后裔。而为同任于同义之地。诚千古奇事也。望明府万加勉旃。以究金公绪馀。而重副多士之愿若何。亭之咏归。金公临归。捐赀付斋儒。俾即营搆。而其亭额则是渼翁手笔。而曾书给鼎焕者也。金公嘱以揭刻楣颜。而荏苒推诿。尚此未焉者。乡之耻也。明府宜其谅嘱。故玆尾及。
年踰七旬。何所求于斯世哉。至于讲学明道。惟以未死为期。然聪明顿铄。如盛漏器。随得随忘。如是而冀其髣髴耶。良可浩叹。先师文敬公。常景仰乎三学士先生。而至先先生忠贞公。尤致缱绻也。往年华宗衮金浦宰。以寒食祀官。见鄙先人于 章陵直中。谓鼎焕密迩渼上语。先人以清阴故事。因出忠贞古镜。相与摩挲久之。要获镜铭于渼翁。而往事已矣。故知府仁瑞氏。以渼翁之孙。而下车先访桐翁墓所在。就其下筑精舍。岁以重九荐菊。多士因推公为洞主。依鹿院故事。方立规听讲。而金公适以事还朝。幽明遽隔。至今乡士所共痛恨也。今明府以同义之后裔。而为同任于同义之地。诚千古奇事也。望明府万加勉旃。以究金公绪馀。而重副多士之愿若何。亭之咏归。金公临归。捐赀付斋儒。俾即营搆。而其亭额则是渼翁手笔。而曾书给鼎焕者也。金公嘱以揭刻楣颜。而荏苒推诿。尚此未焉者。乡之耻也。明府宜其谅嘱。故玆尾及。与李黄州(采)
伏惟新春。道体神相万重。德学俱进。遥不胜钦仰。仆近寓居昌之石冈。就水石构数椽。可以读其中忘其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0H 页
 外矣。如是沉淹岁月。粗有所得。然后乃就质于执事非晚也。而比观南塘跋寒泉诗后之语。思之终有未契者。按朱夫子论生之谓性曰。人与物之异。固由于气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气质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推是而观之则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固由于气禀之不同。则此非气质之性乎。然则尤翁所谓犬牛人之性。亦以气质言也者。乃朱夫子之言也。朱子曰孟子虽不言气质之性。然于告子之谓性之辨。亦既微发其端矣。又于性相近小注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气质之性而言。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然则南塘所云追补未备之意者。盖不免杜撰也。尤翁之意。岂如是哉。南塘曰一原上。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异体上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若果如是。则本然之性二也。气质之性亦二也。此岂尤翁追补之意哉。尤翁所谓气质者。即朱子所谓气禀之不同也。因其气禀之不同。而理亦乘而不同者。气质也。以言乎一原。则万物同具太极者。是本然也。以言乎异体。则万物各一其性者。是气质也。朱子曰天地之性。
外矣。如是沉淹岁月。粗有所得。然后乃就质于执事非晚也。而比观南塘跋寒泉诗后之语。思之终有未契者。按朱夫子论生之谓性曰。人与物之异。固由于气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气质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推是而观之则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固由于气禀之不同。则此非气质之性乎。然则尤翁所谓犬牛人之性。亦以气质言也者。乃朱夫子之言也。朱子曰孟子虽不言气质之性。然于告子之谓性之辨。亦既微发其端矣。又于性相近小注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气质之性而言。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然则南塘所云追补未备之意者。盖不免杜撰也。尤翁之意。岂如是哉。南塘曰一原上。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异体上有本然之性。有气质之性。若果如是。则本然之性二也。气质之性亦二也。此岂尤翁追补之意哉。尤翁所谓气质者。即朱子所谓气禀之不同也。因其气禀之不同。而理亦乘而不同者。气质也。以言乎一原。则万物同具太极者。是本然也。以言乎异体。则万物各一其性者。是气质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0L 页
 即我之性。更无分别彼此。此岂非一原上本然乎。朱子又曰人与物性之异。固由于气禀之不同。又岂非异体上气质乎。若使塘门看本然于一原。而看气质于异体。则其所以同者。天命之流行也。其所以异者。二气之不齐也。孟子之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虽曰已生。为其本然之明。初不相离也。推是而言。则本然之性。人物皆同。而犬牛人性不同者。气质也。非特此章之旨为然。中庸二十二章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乃本然之理同也。大学或问格致条曰但其气质。有人物偏全之殊。此乃异体之气异也。朱子又曰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亲。君臣之相统。间亦有仅存而不昧者。其曰仅存者。果是本然而非气质耶。朱子答徐子融曰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其所以不全者。果亦本然而非气质耶。虽然向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从何处得来耶。朱子曰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然则一原之上。可知其有本然而兼二五之气也。异体之上。可知其有气质而非本然之性也。朱子言理气
即我之性。更无分别彼此。此岂非一原上本然乎。朱子又曰人与物性之异。固由于气禀之不同。又岂非异体上气质乎。若使塘门看本然于一原。而看气质于异体。则其所以同者。天命之流行也。其所以异者。二气之不齐也。孟子之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后。虽曰已生。为其本然之明。初不相离也。推是而言。则本然之性。人物皆同。而犬牛人性不同者。气质也。非特此章之旨为然。中庸二十二章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乃本然之理同也。大学或问格致条曰但其气质。有人物偏全之殊。此乃异体之气异也。朱子又曰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亲。君臣之相统。间亦有仅存而不昧者。其曰仅存者。果是本然而非气质耶。朱子答徐子融曰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其所以不全者。果亦本然而非气质耶。虽然向无本然之性。则此气质之性。从何处得来耶。朱子曰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然则一原之上。可知其有本然而兼二五之气也。异体之上。可知其有气质而非本然之性也。朱子言理气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1H 页
 当离合看。南塘之引而为證者。只在于理同理不同之间。而其所谓离看者一原。而愚之所谓异体也。其所谓合看者异体。而愚之所谓一原也。合看处不离看。(万物一原。理同气异。)离看处又合看。(万物异体。气犹相近。)同中之所异。异中之所同。自有条理。而看文字眼目不同矣。未知执事以为如何。陶庵先生文集校雠之役。已为讫功。而广布于门人知旧处。此何等盛事也。以鼎焕言之则于先生有渊源之可讲。伯父咏归公。尝受学于泉门。不幸早世。妇翁白公东显氏。于先生特蒙奖进。观其赠诗可知也。鼎焕晚未及洒扫于门下。而先师渼湖翁于先生。有道义之契。愚尝讲学于谦斋公丈席。则其所师承尊仰。一而二二而一也。宜其文集之一体同布而不敢望也。苟获此集而晨夕敬玩。有所进益。则亦岂非先生炉韛中物也耶。冒昧及此。不任悚仄。
当离合看。南塘之引而为證者。只在于理同理不同之间。而其所谓离看者一原。而愚之所谓异体也。其所谓合看者异体。而愚之所谓一原也。合看处不离看。(万物一原。理同气异。)离看处又合看。(万物异体。气犹相近。)同中之所异。异中之所同。自有条理。而看文字眼目不同矣。未知执事以为如何。陶庵先生文集校雠之役。已为讫功。而广布于门人知旧处。此何等盛事也。以鼎焕言之则于先生有渊源之可讲。伯父咏归公。尝受学于泉门。不幸早世。妇翁白公东显氏。于先生特蒙奖进。观其赠诗可知也。鼎焕晚未及洒扫于门下。而先师渼湖翁于先生。有道义之契。愚尝讲学于谦斋公丈席。则其所师承尊仰。一而二二而一也。宜其文集之一体同布而不敢望也。苟获此集而晨夕敬玩。有所进益。则亦岂非先生炉韛中物也耶。冒昧及此。不任悚仄。与金承旨(履度)
曾因金生声律。承拜宠覆。比因李明叟胤子。闻执事语及无状。而至咎以贻阻之甚。尽不我遐弃也。如以云泥迥隔而阙然稽谢。则此生已矣。玆替豚儿奉候。伏惟献发。动止茂纳新休。知申有暇。益修家学。德业俱进。是区区悬仰。鼎焕近寓居昌之典岩。起居云山。
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1L 页
 随分读书。足以自娱也。间有庸孟若干劄录。非谓有得也。要以听执事之去取。幸勿孤也否。陶庵中庸讲说。问人物之生。气禀不同。性有偏全之异。故栗谷曰若万物则性不能禀全德。此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然则栗谷之说不是耶。陶庵曰章句就子思本旨而泛论统体。栗谷则就其中细分别出来。虽似不同而实未相悖也。愚窃以为陶庵此答。似涉未莹。中庸首章一原上。理同而气异也。是故朱子于或问曰。在人在天。虽有性命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异。而其理则未尝不一。此非理同而气异者耶。孟子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异体上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是故于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非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栗谷所谓若万物则性不能禀全德者。非谓天命之为然也。乃犬牛人三性之不同。不能禀全德也。问者将此问于犬牛人章则可也。而问于天命之谓性章则不可也。陶庵之不以是答之。而如彼云云者。窃所不敢知也。南塘曰天命之性。人物同与不同。吾于孟子犬牛人章而知
随分读书。足以自娱也。间有庸孟若干劄录。非谓有得也。要以听执事之去取。幸勿孤也否。陶庵中庸讲说。问人物之生。气禀不同。性有偏全之异。故栗谷曰若万物则性不能禀全德。此章句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然则栗谷之说不是耶。陶庵曰章句就子思本旨而泛论统体。栗谷则就其中细分别出来。虽似不同而实未相悖也。愚窃以为陶庵此答。似涉未莹。中庸首章一原上。理同而气异也。是故朱子于或问曰。在人在天。虽有性命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异。而其理则未尝不一。此非理同而气异者耶。孟子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异体上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是故于集注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非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者耶。栗谷所谓若万物则性不能禀全德者。非谓天命之为然也。乃犬牛人三性之不同。不能禀全德也。问者将此问于犬牛人章则可也。而问于天命之谓性章则不可也。陶庵之不以是答之。而如彼云云者。窃所不敢知也。南塘曰天命之性。人物同与不同。吾于孟子犬牛人章而知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2H 页
 之。因證栗谷之说曰物不能禀全德。又引尤翁之说曰物不具五常。此便是医家之用药也。固是药也。而治热之附子。移用于治寒之大黄。则不杀人者几希。以犬牛人章理绝不同者。言之于天命性章理同而气异处。则说不通。以天命性章理同者。言之于犬牛人章理绝不同处。则又岂成说乎。不是之察。而读犬牛人章者。必曰以此观之。人物之性。岂非不同者耶。读天命性者。必曰人物之性。岂非皆同者欤。非独此章之旨为然也。大学或问曰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此岂非理同而气异者耶。论语性相近小注曰。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亦指气质而言也者。此乃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我东诸老先生言皆如此。栗谷论中庸首章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曰。理气元不相离。即气而理在其中。此承阴阳化生而言。故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非谓有气而后有理也。此言理同而气异也。愚伏论孟子犬牛人性章曰。犬牛性之不善。非生不得夫天理也。此皆气之为也。此言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尤翁曰犬牛人性之不同。气质也。南塘独以为本然而非
之。因證栗谷之说曰物不能禀全德。又引尤翁之说曰物不具五常。此便是医家之用药也。固是药也。而治热之附子。移用于治寒之大黄。则不杀人者几希。以犬牛人章理绝不同者。言之于天命性章理同而气异处。则说不通。以天命性章理同者。言之于犬牛人章理绝不同处。则又岂成说乎。不是之察。而读犬牛人章者。必曰以此观之。人物之性。岂非不同者耶。读天命性者。必曰人物之性。岂非皆同者欤。非独此章之旨为然也。大学或问曰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此岂非理同而气异者耶。论语性相近小注曰。孟子所谓犬牛人性之殊。亦指气质而言也者。此乃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我东诸老先生言皆如此。栗谷论中庸首章气以成形理亦赋焉曰。理气元不相离。即气而理在其中。此承阴阳化生而言。故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非谓有气而后有理也。此言理同而气异也。愚伏论孟子犬牛人性章曰。犬牛性之不善。非生不得夫天理也。此皆气之为也。此言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尤翁曰犬牛人性之不同。气质也。南塘独以为本然而非典庵文集卷之四 第 632L 页
 气质者。误看此章之为理同也。盖理气之说。自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中出来。凡看理气。不以此为准则。浩浩茫茫。无处下手。今乃湖曰洛非。洛曰湖非。转辗相激。殆同同室操戈者。吾道之不幸甚矣。未知执事以为如何。荛言之如有丑差。则幸驳教之也。
气质者。误看此章之为理同也。盖理气之说。自朱子所谓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中出来。凡看理气。不以此为准则。浩浩茫茫。无处下手。今乃湖曰洛非。洛曰湖非。转辗相激。殆同同室操戈者。吾道之不幸甚矣。未知执事以为如何。荛言之如有丑差。则幸驳教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