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序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0H 页
 奉寿㓒溪先生母夫人赵氏八十岁序(辛▣)
奉寿㓒溪先生母夫人赵氏八十岁序(辛▣)不佞自丱角时。游于先生所。每见先生事母夫人悦之。先生只居殆二十年馀。内无议酒食者。则其孝于母夫人。亦难矣哉。于是有弟若子贤。代先生供奉宜无憾。犹且以为惟我职。惟大夫人寒暑饥饱以时。躬枕簟膏毳。如烹饪鼎俎。乃妇人事。虽委之子弟妇。亦不乐也。尝语不佞曰。我早无妻且病。于子道不能万之一。是天不孝我也。穷而贫。大夫养无论。渔樵承欢。可以自勉焉。不佞且以悲之。先生尽于孝若此。犹戚戚然不自足。子之道信无穷矣。传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古之大孝也。而且以为可。先生学曾子者也。其所以为心。固无足怪。然使先生无疾病丧乱之毒。则其用力于事亲者有万万。彼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者。其孝于亲。果何如也。苞苴权贵。惟觊觎是急。其一时三牲之养。不足为孝。先生于此。宜有所浼焉者。虽以不能尽其孝为恨。而在今世亦庶几子道矣。惟其天之割于先生者。不可知也。虽然。大夫人春秋业八十。精强善匙筋。以享其孝养。夫人之有父母也。莫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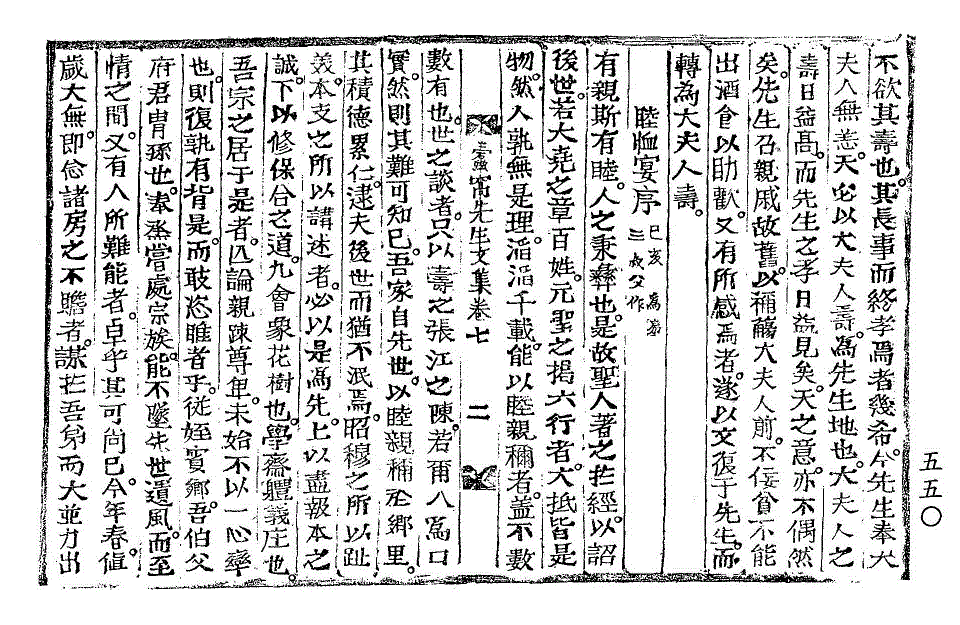 不欲其寿也。其长事而终孝焉者几希。今先生奉大夫人无恙。天必以大夫人寿。为先生地也。大夫人之寿日益高。而先生之孝日益见矣。天之意。亦不偶然矣。先生召亲戚故旧。以称觞大夫人前。不佞贫不能出酒食以助欢。又有所感焉者。遂以文复于先生。而转为大夫人寿。
不欲其寿也。其长事而终孝焉者几希。今先生奉大夫人无恙。天必以大夫人寿。为先生地也。大夫人之寿日益高。而先生之孝日益见矣。天之意。亦不偶然矣。先生召亲戚故旧。以称觞大夫人前。不佞贫不能出酒食以助欢。又有所感焉者。遂以文复于先生。而转为大夫人寿。睦恤宴序(己亥○为第三叔父作)
有亲斯有睦。人之秉彝也。是故圣人著之于经。以诏后世。若大尧之章百姓。元圣之揭六行者。大抵皆是物。然人孰无是理。滔滔千载。能以睦亲称者。盖不数数有也。世之谈者。只以寿之张江之陈。若尔人为口实。然则其难可知已。吾家自先世。以睦亲称于乡里。其积德累仁。逮夫后世而犹不泯焉。昭穆之所以趾美。本支之所以讲述者。必以是为先。上以尽报本之诚。下以修保合之道。九会象花树也。学斋体义庄也。吾宗之居于是者。亡论亲疏尊卑。未始不以一心率也。则复孰有背是。而敢恣睢者乎。从侄宾乡。吾伯父府君胄孙也。奉烝尝处宗族。能不坠先世遗风。而至情之间。又有人所难能者。卓乎其可尚已。今年春。值岁大无。即念诸房之不赡者。谋于吾弟而大并力出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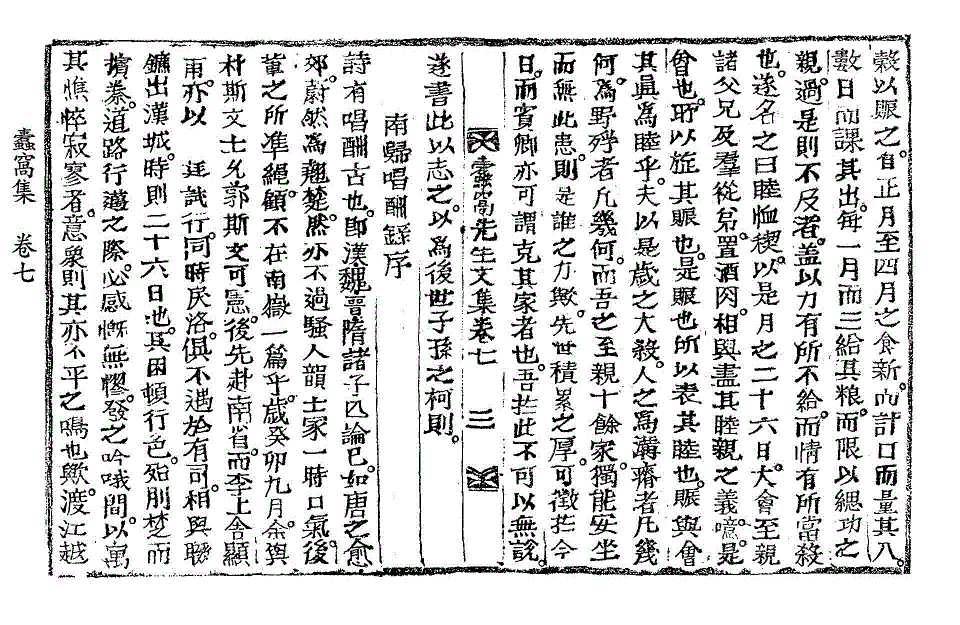 谷以赈之。自正月至四月之食新。而计口而量其入。数日而课其出。每一月而三给其粮。而限以缌功之亲。过是则不及者。盖以力有所不给。而情有所当杀也。遂名之曰睦恤稧。以是月之二十六日。大会至亲诸父兄及群从弟。置酒肉。相与尽其睦亲之义。噫。是会也。所以㫌其赈也。是赈也。所以表其睦也。赈与会其真为睦乎。夫以是岁之大杀。人之为沟瘠者凡几何。为野殍者凡几何。而吾之至亲十馀家。独能安坐而无此患。则是谁之力欤。先世积累之厚。可徵于今日。而宾卿亦可谓克其家者也。吾于此不可以无说。遂书此以志之。以为后世子孙之柯则。
谷以赈之。自正月至四月之食新。而计口而量其入。数日而课其出。每一月而三给其粮。而限以缌功之亲。过是则不及者。盖以力有所不给。而情有所当杀也。遂名之曰睦恤稧。以是月之二十六日。大会至亲诸父兄及群从弟。置酒肉。相与尽其睦亲之义。噫。是会也。所以㫌其赈也。是赈也。所以表其睦也。赈与会其真为睦乎。夫以是岁之大杀。人之为沟瘠者凡几何。为野殍者凡几何。而吾之至亲十馀家。独能安坐而无此患。则是谁之力欤。先世积累之厚。可徵于今日。而宾卿亦可谓克其家者也。吾于此不可以无说。遂书此以志之。以为后世子孙之柯则。南归唱酬录序
诗有唱酬古也。即汉,魏,晋,隋诸子亡论已。如唐之愈,郊。蔚然为翘楚。然亦不过骚人韵士家一时口气。后辈之所准绳。顾不在南岳一篇乎。岁癸卯九月。余与朴斯文士允,郭斯文可宪。后先赴南省。而李上舍显甫。亦以 廷试行。同时戾洛。俱不遇于有司。相与联镳出汉城。时则二十六日也。其困顿行色。殆刖楚而摈秦。道路行迈之际。必感慨无憀。发之吟哦间。以寓其憔悴寂寥者。意象则其亦不平之鸣也欤。渡江越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1L 页
 四日。取路晴川而行。盖同行诸人。皆有一见俗离之愿。遂逶迤造山门。山日才三四竿。卸鞍不发。周览一山形胜。翌日出山。又越五日而到大桥店。各分袂归家。留约更会于可宪家。及期俱往。吴君元宾,载宾,郭甥圣能亦末至。与觚翰之政。留连数日而罢。噫。是役也首尾凡十馀日。而或登山临水。或阻雨滞风。或早发晚行。无不记之诗中。而落拓轮囷之语。辄居其二三。则是知一番得丧。系着在肚里。有不得消磨尽。上蔡所谓透得名利关。方是少休歇处者。正为吾辈顶门上一针。然士生斯世。其抱负不少。泯泯与草木同腐。岂所欲哉。既有命。不可以戾契取。则乃以童马筇屐。超然独往于名山大川之间。与神仙者流。逍遥乎汗漫。翱翔乎蔚蓝。得烟云霞岚之变态。而换状者。津津在牙颊。则俯视尘世间区区俗子。是垤蚁而醯鸡而采真天游。于是焉朝暮遇。吾辈所得不既多矣乎。诗令自东字至咸字。节次押去。而每篇以不遗元韵为凡例。又以诗成先后为长第。篇下各书表德一字以识之。长短近体各几首。古体各几首。联句凡几首。而蒸字以下。则可宪家所赋也。遂脱稿登卷。以为他日破閒之资。若使吾辈得志曩者。将无是游。不偶于
四日。取路晴川而行。盖同行诸人。皆有一见俗离之愿。遂逶迤造山门。山日才三四竿。卸鞍不发。周览一山形胜。翌日出山。又越五日而到大桥店。各分袂归家。留约更会于可宪家。及期俱往。吴君元宾,载宾,郭甥圣能亦末至。与觚翰之政。留连数日而罢。噫。是役也首尾凡十馀日。而或登山临水。或阻雨滞风。或早发晚行。无不记之诗中。而落拓轮囷之语。辄居其二三。则是知一番得丧。系着在肚里。有不得消磨尽。上蔡所谓透得名利关。方是少休歇处者。正为吾辈顶门上一针。然士生斯世。其抱负不少。泯泯与草木同腐。岂所欲哉。既有命。不可以戾契取。则乃以童马筇屐。超然独往于名山大川之间。与神仙者流。逍遥乎汗漫。翱翔乎蔚蓝。得烟云霞岚之变态。而换状者。津津在牙颊。则俯视尘世间区区俗子。是垤蚁而醯鸡而采真天游。于是焉朝暮遇。吾辈所得不既多矣乎。诗令自东字至咸字。节次押去。而每篇以不遗元韵为凡例。又以诗成先后为长第。篇下各书表德一字以识之。长短近体各几首。古体各几首。联句凡几首。而蒸字以下。则可宪家所赋也。遂脱稿登卷。以为他日破閒之资。若使吾辈得志曩者。将无是游。不偶于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2H 页
 世者。不害为江山之偶。遂书此以弁其卷。
世者。不害为江山之偶。遂书此以弁其卷。万进堂诗序
尝观 皇明之末。有嘉兴高寓公者。崇祯庚辰进士。逮弘光乙酉。见国家沦丧。自屏于草野。作诗述志曰。惟将前进士。惨惔表孤坟。遂呼愤抑殁而死。噫。寓公其烈丈夫乎。当是时。怀忠抱义如寓公者。凡几人哉。自嘉兴。东走凡几万里。得朝鲜之苞山郭万进先生。尝以万历丁巳。举本国进士。当崇祯丙子。本国有城下之役。而天下且帝秦矣。则于是乎先生慨然深耻。无复有当世意。撰次 皇明记。因题一句曰。晦盲否塞人何世。万进堂中日月明。遂自号万进。隐约以毕世焉。先生之必以万进颜其堂者。其亦寓公表坟之意乎。地之相去若是其辽阔。而不先不后。有若同车携手者然。又何其奇哉。彼寓公者。中州士也。以相韩家世身。且尝备法从矣。则其悲歌痛哭。以泄其忠愤固也。先生藐然以东国之一书生。生长于大海之滨。巨岭之表。去中国万有馀里。步武一未尝蹑 皇都也。眼孔一未尝觐耿光也。则其于 皇朝即无有一命沾丐之恩。犹且乃尔。以七尺微躯。担荷万古纲常之重。岂不是尤卓然哉。君臣父子之伦。不以地之远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2L 页
 近内外而有所或间。于此可见。韩子所谓强仁慕义。出于其性者哉。朱夫子所谓天之经地之纪。为人之秉彝者哉。然则先生非特为朝鲜烈士。乃天下之烈士也。夫惟我东国。即殷父师罔仆之遗墟。而宣尼之所欲居也。鲁连之所欲蹈也。则先生之出于其间。岂徒然哉。今其诗特寂寥一句耳。使人讽之。声韵悲壮。志气凛烈。隐然有发风冽泉之思。其元遗山,谢皋羽之遗音乎。其姚平仲,张惟孝,龙可伯,赵九龄之同调乎。其高忠孤愤。可以撑宇宙而骈日月。作一天地间间气希宝。有如颓波之砥柱。烈炎之昆玉。则岂特曰诗而已哉。钱虞山惨然以周遗夏隶。叙述当时之士。而特于寓公详焉。既立其家传。又序其遗诗曰。高氏累世忠义。辉映简册。垂三百年。先生家且然。自清白公以至定庵,存斋,忘忧公。皆以忠义著。先生盖有所受之也。若使虞山得闻先生之风。岂不欲褰裳浿水。张眼而吐胆。如皇甫及陈昌箕乎。又岂不大书特书于崇祯野乘之末曰。朝鲜有明处士郭某。如纲目之书陶潜乎。否则传而序之。以铺张其事。当如高寓公的矣。余方竹栊风檐。展读先生诗。起而望中原天。醉尚未醒。若有一段光怪攒复。陆离于西北间。是殆先
近内外而有所或间。于此可见。韩子所谓强仁慕义。出于其性者哉。朱夫子所谓天之经地之纪。为人之秉彝者哉。然则先生非特为朝鲜烈士。乃天下之烈士也。夫惟我东国。即殷父师罔仆之遗墟。而宣尼之所欲居也。鲁连之所欲蹈也。则先生之出于其间。岂徒然哉。今其诗特寂寥一句耳。使人讽之。声韵悲壮。志气凛烈。隐然有发风冽泉之思。其元遗山,谢皋羽之遗音乎。其姚平仲,张惟孝,龙可伯,赵九龄之同调乎。其高忠孤愤。可以撑宇宙而骈日月。作一天地间间气希宝。有如颓波之砥柱。烈炎之昆玉。则岂特曰诗而已哉。钱虞山惨然以周遗夏隶。叙述当时之士。而特于寓公详焉。既立其家传。又序其遗诗曰。高氏累世忠义。辉映简册。垂三百年。先生家且然。自清白公以至定庵,存斋,忘忧公。皆以忠义著。先生盖有所受之也。若使虞山得闻先生之风。岂不欲褰裳浿水。张眼而吐胆。如皇甫及陈昌箕乎。又岂不大书特书于崇祯野乘之末曰。朝鲜有明处士郭某。如纲目之书陶潜乎。否则传而序之。以铺张其事。当如高寓公的矣。余方竹栊风檐。展读先生诗。起而望中原天。醉尚未醒。若有一段光怪攒复。陆离于西北间。是殆先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3H 页
 生之灵。与寓公诸人。相遇于汗漫赫曦之上。有以现化其精爽者乎。遂援笔感慨而状其行。仍为之诗序。其有不灭者存。必将以余为海东之虞山也已。
生之灵。与寓公诸人。相遇于汗漫赫曦之上。有以现化其精爽者乎。遂援笔感慨而状其行。仍为之诗序。其有不灭者存。必将以余为海东之虞山也已。吴氏遗墨帖序
此帖上下。凡十六叠。乃竹牖敬庵两先生遗笔也。先生父子。俱以笔名。即与右军家奚让。然此特其馀。本之则有大焉。姑就其笔而评之。瘦硬高古。如长松老桧。皮尽而骨露者。竹牖笔也。浓丽活动。如苍藤碧萝枝交而影密者。敬庵笔也。东坡所谓玉环飞燕。各有态者非耶。其子孙旧以为屏八叠而两世之笔。传之屏前后。若乔梓然。其亦彪炳世烈哉。惟其岁既久。阅览者且多。点污毁坏。难保其必无。吴君载宾以是之惧。刬取其屏面墨本。褙以新纸。妆以锦匣而藏弆之。可谓孝子慈孙之所用心也。日余过其庐。载宾出示此帖。属余叙其颠末。余遂谂之曰。敦牟卮匜。器耳。巾屦枕簟。服耳。为子孙者。犹且爱敬而不敢慢。况此帖之出于其心画者乎。此帖在吴氏家。殆兰亭之茧纸。吴兴之绢裙。其为传家宝藏。与寻常手泽。不倍筛翅矣。虽然。其所以守之者。有本有末。苟物而已则抑末之焉。尝闻祖考之精神。即我之精神。盖其一气流通。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3L 页
 虽千百岁远。能致我爱敬之实。即著而存者在耳。载宾之观此帖也。无徒区区于其末。必就其精神贯注处。因其书而求其心。以无忝尔所自生。则寔能为保家主。奚特保此帖而已哉。然人家子孙之有贤不肖。异思固也。君安知后世无三虫者出。而货视此帖耶。今夫思发于心而心贵乎得其正。君其以此诏后曰。勿心其自心。而必心以先祖之心云尔。则庶乎其可也。载宾起而复曰敬闻命。遂书此以归之。载宾竹牖先生八世孙也。
虽千百岁远。能致我爱敬之实。即著而存者在耳。载宾之观此帖也。无徒区区于其末。必就其精神贯注处。因其书而求其心。以无忝尔所自生。则寔能为保家主。奚特保此帖而已哉。然人家子孙之有贤不肖。异思固也。君安知后世无三虫者出。而货视此帖耶。今夫思发于心而心贵乎得其正。君其以此诏后曰。勿心其自心。而必心以先祖之心云尔。则庶乎其可也。载宾起而复曰敬闻命。遂书此以归之。载宾竹牖先生八世孙也。玉峰实记序
此故处士卢公实纪也。号以玉峰何。公居玉峰下。乡人以是为公号也。公不自号。而乡人号公何。艳公之行而高之。不以其名而号以其居。古人私谥之遗法也。公之孙士默甫。尝缄是卷来。辱命以弁首之文曰。王父平生。尽在于是。愿有以商之。余辞以非其人。顾强之愈勤。谨受而卒业。恨生齵不及一望公颜色。然读是卷。可以得其实矣。当时及后来。亡论识与不识。所以称述之者。无异辞。无实而能然乎。光闇而必章。声默而必闻。固其理也。然实已存乎已。又何待是卷徵诸久而信于后。非是则不可。昔董生召南隐约以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4H 页
 殁于桐柏山中。而行义至今著简策。特以昌黎氏一序一诗在故也。不然。安丰之一渔樵耳。今卷中诸名胜。其言皆足以发挥。况艮翁李尚书。乃当世词伯。又为之铭墓。其取重传信必矣。为孝子慈孙者。其于保是卷。当何如哉。顾余不腆。诚无所损益。然重孤勤意。谨书此以复之。
殁于桐柏山中。而行义至今著简策。特以昌黎氏一序一诗在故也。不然。安丰之一渔樵耳。今卷中诸名胜。其言皆足以发挥。况艮翁李尚书。乃当世词伯。又为之铭墓。其取重传信必矣。为孝子慈孙者。其于保是卷。当何如哉。顾余不腆。诚无所损益。然重孤勤意。谨书此以复之。南皋忠愤诗后序
当宋亡而元主中国。独有刘静修一人以伯夷称。彼中华大地。一何其寥寥哉。气数翻覆之际。草野无禄位者。能办大节。若是其难矣。是故。 皇明沦丧。钱虞山叙述皇甫及高寓公之伦甚详。亦廑廑耳。至若我国则当是时。秉尊周耻帝秦者。项背相望。区区外服。诚可谓炳烺。不有 先王之教培养得厚。乌能若是。况粤若 圣祖。尝于禁籞中。筑大报坛。以寓夫江汉遗思。上有好而下必甚。亦可徵焉尔。灵川有朴南皋先生。即其一也。今按先生忠愤诗。自丙子至乙酉。皆伤时愤世之作。而志气慷慨。声韵浏湸。隐然有折冲樽俎之意象。观于此。固知为烈丈夫。独诗乎哉。平生铲迹深山中。自处以崇祯遗民。时或酒后耳热。则拊釰而歌。歌竟辄西望痛哭。以泄其忠愤。此诗所以志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4L 页
 也。噫。先生东国一士耳。距中国万里以遥。何尝于 皇明。有一豪沾溉恩。犹且尔焉。夫所谓天经地纪。不以华裔限。不以显微隔者。有如是夫。虽然。是岂无自而然。先生鹤岩先生孙也。鹤岩公当壬辰岛夷乱。倡大义以讨贼。发家财以饷 天朝诸将士。先生盖有所受之矣。忠义世其家。虽以海外匹夫。西归一念。岂渠在曹桧士下哉。窃伏闻今我 圣上命词臣撰尊攘录。亡论荐绅韦布。凡义关崇祯事者。无不收采。盖继述之意也。如先生诗。虽大书而特书。亦无愧焉。吾知当世之执木天笔者。必有取于斯乎。
也。噫。先生东国一士耳。距中国万里以遥。何尝于 皇明。有一豪沾溉恩。犹且尔焉。夫所谓天经地纪。不以华裔限。不以显微隔者。有如是夫。虽然。是岂无自而然。先生鹤岩先生孙也。鹤岩公当壬辰岛夷乱。倡大义以讨贼。发家财以饷 天朝诸将士。先生盖有所受之矣。忠义世其家。虽以海外匹夫。西归一念。岂渠在曹桧士下哉。窃伏闻今我 圣上命词臣撰尊攘录。亡论荐绅韦布。凡义关崇祯事者。无不收采。盖继述之意也。如先生诗。虽大书而特书。亦无愧焉。吾知当世之执木天笔者。必有取于斯乎。李通彦游枫岳序
世传三神山俱在东海上。盖枫岳即其一也。佛曰金刚。仙曰蓬壶者是已。其瑰奇绝特之观。甲天下。又有珍卉异草可以饵而不死者。多在其中云。所谓列真府众香城无则已。有也必此山。所以华人有结他生一见之愿。而至于脱万乘捐四海。褰裳而欲从者亦往往。然而稗语曰。舟近山下。风辄引去。无乃无仙根佛种。有所呵禁者存欤。此吊诡不足信。而山固灵怪矣哉。广陵李通彦于山水。有土炭嗜。凡穷崖绝壑。茂林邃谷。苟有可偿者。无不恣搜博访。必望其腹而后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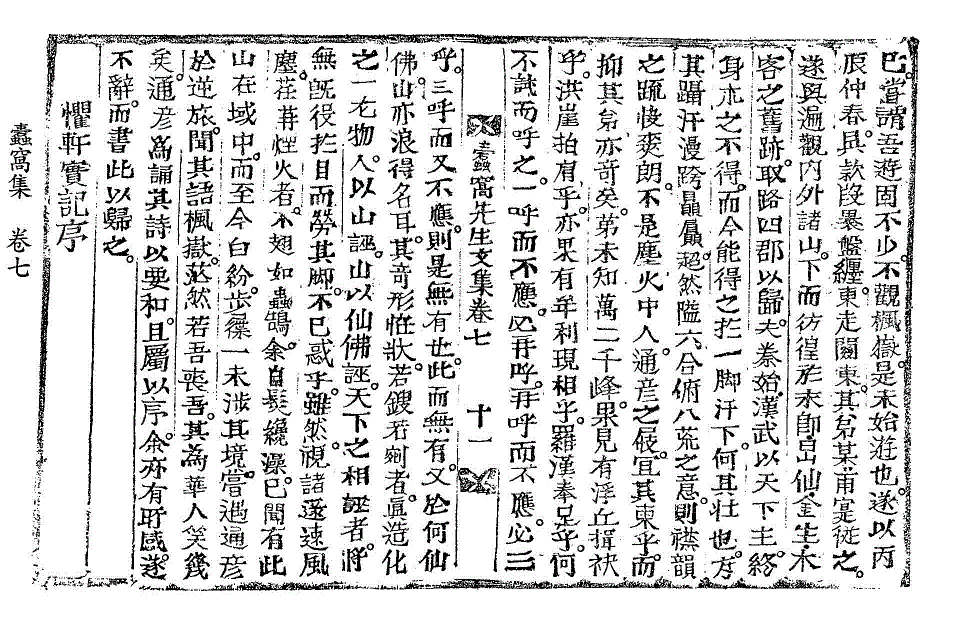 已。尝谓吾游固不少。不观枫岳。是未始游也。遂以丙辰仲春。具款段裹盘缠。东走关东。其弟某甫寔从之。遂与遍观内外诸山。下而彷徨于永郎,旵仙,金生,木客之旧迹。取路四郡以归。夫秦始,汉武以天下主。终身求之不得。而今能得之于一脚汗下。何其壮也。方其蹑汗漫跨赑屃。超然隘六合俯八荒之意。则襟韵之疏快爽朗。不是尘火中人。通彦之屐。宜其东乎。而抑其弟亦奇矣。第未知万二千峰。果见有浮丘揖袂乎。洪崖拍肩乎。亦果有牟利现相乎。罗汉奉足乎。何不试而呼之。一呼而不应。必再呼。再呼而不应。必三呼。三呼而又不应。则是无有也。此而无有。又于何仙佛。山亦浪得名耳。其奇形怪状。若锼若剜者。真造化之一尤物。人以山诬。山以仙佛诬。天下之相诬者。将无既役于目而劳其脚。不已惑乎。虽然。视诸逯速风尘。荏苒烟火者。不翅如虫鹄。余自发才澡。已闻有此山在域中。而至今白纷。步屧一未涉其境。尝遇通彦于逆旅。闻其语枫岳。茫然若吾丧吾。其为华人笑几矣。通彦为诵其诗以要和。且属以序。余亦有所感。遂不辞。而书此以归之。
已。尝谓吾游固不少。不观枫岳。是未始游也。遂以丙辰仲春。具款段裹盘缠。东走关东。其弟某甫寔从之。遂与遍观内外诸山。下而彷徨于永郎,旵仙,金生,木客之旧迹。取路四郡以归。夫秦始,汉武以天下主。终身求之不得。而今能得之于一脚汗下。何其壮也。方其蹑汗漫跨赑屃。超然隘六合俯八荒之意。则襟韵之疏快爽朗。不是尘火中人。通彦之屐。宜其东乎。而抑其弟亦奇矣。第未知万二千峰。果见有浮丘揖袂乎。洪崖拍肩乎。亦果有牟利现相乎。罗汉奉足乎。何不试而呼之。一呼而不应。必再呼。再呼而不应。必三呼。三呼而又不应。则是无有也。此而无有。又于何仙佛。山亦浪得名耳。其奇形怪状。若锼若剜者。真造化之一尤物。人以山诬。山以仙佛诬。天下之相诬者。将无既役于目而劳其脚。不已惑乎。虽然。视诸逯速风尘。荏苒烟火者。不翅如虫鹄。余自发才澡。已闻有此山在域中。而至今白纷。步屧一未涉其境。尝遇通彦于逆旅。闻其语枫岳。茫然若吾丧吾。其为华人笑几矣。通彦为诵其诗以要和。且属以序。余亦有所感。遂不辞。而书此以归之。惧轩实记序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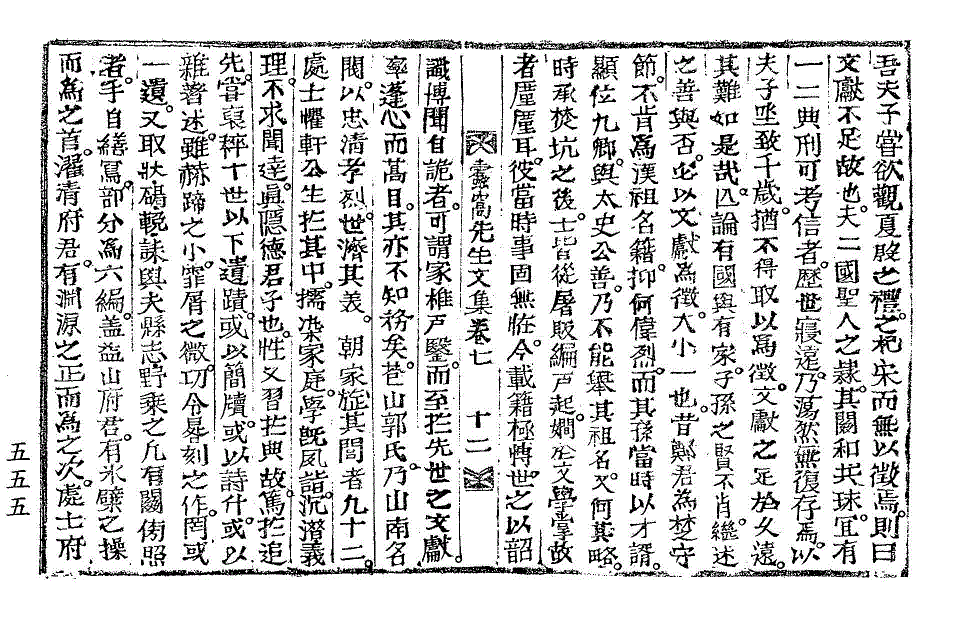 吾夫子尝欲观夏殷之礼。之杞宋而无以徵焉。则曰文献不足故也。夫二国圣人之隶。其关和共球。宜有一二典刑可考信者。历世寝远。乃荡然无复存焉。以夫子坐致千岁。犹不得取以为徵。文献之定于久远。其难如是哉。亡论有国与有家。子孙之贤不肖。继述之善与否。必以文献为徵。大小一也。昔郑君为楚守节。不肯为汉祖名籍。抑何伟烈。而其孙当时以才谞。显位九卿。与太史公善。乃不能举其祖名。又何其略。时承焚坑之后。士皆从屠贩编户起。娴于文学掌故者廑廑耳。彼当时事固无怪。今载籍极博。世之以韶识博闻自诡者。可谓家椎户凿。而至于先世之文献。率蓬心而蒿目。其亦不知务矣。苞山郭氏。乃山南名阀。以忠清孝烈。世济其美。 朝家㫌其闾者凡十二。处士惧轩公生于其中。擩染家庭。学既夙诣。沉潜义理。不求闻达。真隐德君子也。性又习于典故。笃于追先。尝裒稡十世以下遗迹。或以简牍。或以诗什。或以杂著述。虽赫蹄之小。霏屑之微。功令晷刻之作。罔或一遗。又取状,碣,挽,诔与夫县志,野乘之凡有关傍照者。手自缮写。部分为六编。盖益山府君。有冰檗之操而为之首。濯清府君。有渊源之正而为之次。处士府
吾夫子尝欲观夏殷之礼。之杞宋而无以徵焉。则曰文献不足故也。夫二国圣人之隶。其关和共球。宜有一二典刑可考信者。历世寝远。乃荡然无复存焉。以夫子坐致千岁。犹不得取以为徵。文献之定于久远。其难如是哉。亡论有国与有家。子孙之贤不肖。继述之善与否。必以文献为徵。大小一也。昔郑君为楚守节。不肯为汉祖名籍。抑何伟烈。而其孙当时以才谞。显位九卿。与太史公善。乃不能举其祖名。又何其略。时承焚坑之后。士皆从屠贩编户起。娴于文学掌故者廑廑耳。彼当时事固无怪。今载籍极博。世之以韶识博闻自诡者。可谓家椎户凿。而至于先世之文献。率蓬心而蒿目。其亦不知务矣。苞山郭氏。乃山南名阀。以忠清孝烈。世济其美。 朝家㫌其闾者凡十二。处士惧轩公生于其中。擩染家庭。学既夙诣。沉潜义理。不求闻达。真隐德君子也。性又习于典故。笃于追先。尝裒稡十世以下遗迹。或以简牍。或以诗什。或以杂著述。虽赫蹄之小。霏屑之微。功令晷刻之作。罔或一遗。又取状,碣,挽,诔与夫县志,野乘之凡有关傍照者。手自缮写。部分为六编。盖益山府君。有冰檗之操而为之首。濯清府君。有渊源之正而为之次。处士府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6H 页
 君。有文艺之俱绝而为之第三。沿之以降。洛叟公之忠义奋厉也。司勇公之寿考康宁也。礼圃公之风采隽伟也。大隐公之才调赡华也。六编之中。昭穆以序。乔梓相应。灿若珠玑错落。烂若云霞蔚纡。吁其盛矣。此殆苞山氏之一部掌故。而数东南文献之传。宜其偻第一指也。在宋朝。吕氏有八代家传。在皇明。华氏有七贤遗像。而考亭夫子,弇山翁。皆以文献之盛归之。今公之家。岂渠逊二氏下哉。日郭君师俊。赉一本逸稿以授不佞曰。此吾曾王考平昔咳唾之馀。而伯季从大父所尝汇辑而誊传者也。愿子之有以商之而惠一言。以弁其首。顾不佞苞山氏自出。于公为近属。亦尝纳拜床下。而辱知奖甚腆。义有不得辞者。遂擎而复曰。噫甚矣。其速肖也。是稿也其体裁规抚。视诸向六编者。无一之差爽。亦可谓善于箕裘。而能于封殖者欤。诗曰。无念尔祖。公实有焉。又曰式谷似之。公之子若孙其庶几。吾知异日者。必有观礼君子来而取徵于文献。又何患不能奉大父讳以属太史氏。铺张如当时者。第不佞笔力。无以望考亭夫子弇山翁之脚汗。为可恨耳。姑书此归之。以为惧轩公实纪序。
君。有文艺之俱绝而为之第三。沿之以降。洛叟公之忠义奋厉也。司勇公之寿考康宁也。礼圃公之风采隽伟也。大隐公之才调赡华也。六编之中。昭穆以序。乔梓相应。灿若珠玑错落。烂若云霞蔚纡。吁其盛矣。此殆苞山氏之一部掌故。而数东南文献之传。宜其偻第一指也。在宋朝。吕氏有八代家传。在皇明。华氏有七贤遗像。而考亭夫子,弇山翁。皆以文献之盛归之。今公之家。岂渠逊二氏下哉。日郭君师俊。赉一本逸稿以授不佞曰。此吾曾王考平昔咳唾之馀。而伯季从大父所尝汇辑而誊传者也。愿子之有以商之而惠一言。以弁其首。顾不佞苞山氏自出。于公为近属。亦尝纳拜床下。而辱知奖甚腆。义有不得辞者。遂擎而复曰。噫甚矣。其速肖也。是稿也其体裁规抚。视诸向六编者。无一之差爽。亦可谓善于箕裘。而能于封殖者欤。诗曰。无念尔祖。公实有焉。又曰式谷似之。公之子若孙其庶几。吾知异日者。必有观礼君子来而取徵于文献。又何患不能奉大父讳以属太史氏。铺张如当时者。第不佞笔力。无以望考亭夫子弇山翁之脚汗。为可恨耳。姑书此归之。以为惧轩公实纪序。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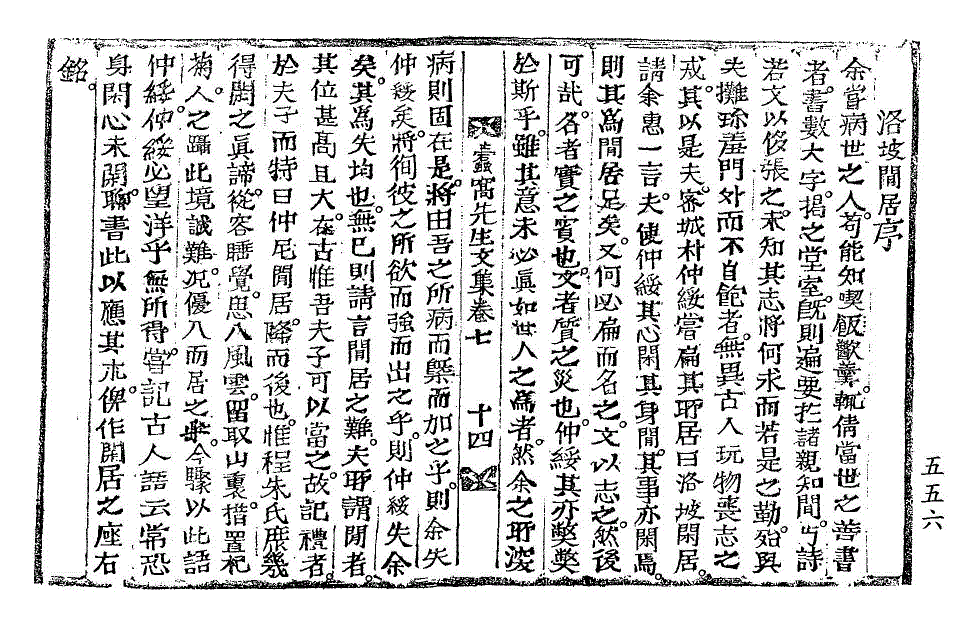 洛坡閒居序
洛坡閒居序余尝病世之人。苟能知吃饭歠羹。辄倩当世之善书者。书数大字。揭之堂室。既则遍要于诸亲知间。丐诗若文以侈张之。未知其志将何求而若是之勤。殆与夫摊珍羞门外而不自饱者。无异古人玩物丧志之戒。其以是夫。密城朴仲绥尝扁其所居曰洛坡闲居。请余惠一言。夫使仲绥其心闲其身閒。其事亦闲焉。则其为閒居足矣。又何必扁而名之。文以志之。然后可哉。名者实之宾也。文者质之灾也。仲绥其亦弊弊于斯乎。虽其意未必真如世人之为者。然余之所深病则固在是。将由吾之所病而槩而加之乎。则余失仲绥矣。将徇彼之所欲而强而出之乎。则仲绥失余矣。其为失均也。无已则请言閒居之难。夫所谓閒者。其位甚高且大。在古惟吾夫子可以当之。故记礼者。于夫子而特曰仲尼閒居。降而后也。惟程朱氏庶几得闲之真谛。从容睡觉。思入风云。留取山里。措置杞菊。人之蹑此境诚难。况优入而居之乎。今骤以此语仲绥。仲绥必望洋乎无所得。尝记古人语云常恐身闲心未闲。聊书此以应其求。俾作闲居之座右铭。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7H 页
 无忝录序
无忝录序人亡论家国。必取徵于文献。自夫子始。当时杞宋之叹。特伤其为夏肄殷绪耳。夫夏非我所自出。固末如于不足。既自曰殷人也。则是乌可但已乎。于易必得其坤乾。于礼必善其葬而祔。于诗。必次其正考父所得。颂以附诸三百篇。后圣人之勤于先世。亦可知已。然则能足其文献。俾后人徵固难。既足矣又徵矣。而能不愧为尤难。顾不系乎子孙之贤不肖何如耶。是故自汉以来。荐绅学士。皆知重掌故。如迁固,雄,机,岳,信之伦。率序次成一家言。岂不诚彪炳乎。而或亏其形体。或坠其名节。以玷其先世。则何有于文献哉。惟北朝颜氏有一家训。龙门王氏有六世述。金华吕氏有八代传。鸿山华氏有七贤像。后之尚论者。必以文献之盛许之。庶几乎夫子所谓足则能徵。其亦贤矣。莼城朴君国祯。尝裒稡其先世遗事。先之以内外派系考妣行录。而凡邑志国乘之有关旁照者。逐世采附。次之以状,叙,碣,志及父师之训,题咏之什。又次之以当时诸名胜投赠唱酬序记颂祝挽诔等作。汇为三大编。名之曰无忝录。盖取诸小宛诗第四章之义也。日国祯过余而命之序。继以书来属益勤。余与国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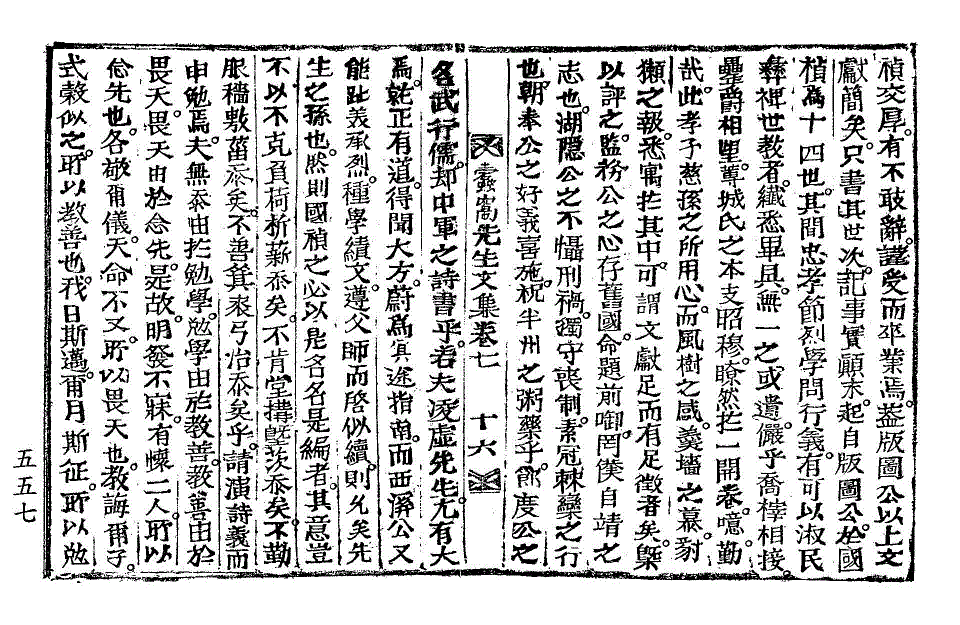 祯交厚。有不敢辞。谨受而卒业焉。盖版图公以上文献简矣。只书其世次。记事实颠末。起自版图公。于国祯为十四世。其间忠孝节烈学问行义。有可以淑民彝裨世教者。纤悉毕具。无一之或遗。俨乎乔梓相接。罍爵相望。莼城氏之本支昭穆。瞭然于一开卷。噫。勤哉。此孝子慈孙之所用心。而风树之感。羹墙之慕。豺獭之报。悉寓于其中。可谓文献足而有足徵者矣。槩以评之。监务公之心存旧国。命题前衔。罔仆自靖之志也。湖隐公之不慑刑祸。独守丧制。素冠棘栾之行也。朝奉公之好义喜施。祝半州之粥药乎。节度公之名武行儒。却中军之诗书乎。若夫凌虚先生。尤有大焉。就正有道。得闻大方。蔚为冥途指南。而西溪公又能趾美承烈。种学绩文。遵父师而启似续。则允矣先生之孙也。然则国祯之必以是名名是编者。其意岂不以不克负荷析薪忝矣。不肯堂搆塈茨忝矣。不勤服穑敷菑忝矣。不善箕裘弓冶忝矣乎。请演诗义而申勉焉。夫无忝由于勉学。勉学由于教善。教善由于畏天。畏天由于念先。是故。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所以念先也。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所以畏天也。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所以教善也。我日斯迈。尔月斯征。所以勉
祯交厚。有不敢辞。谨受而卒业焉。盖版图公以上文献简矣。只书其世次。记事实颠末。起自版图公。于国祯为十四世。其间忠孝节烈学问行义。有可以淑民彝裨世教者。纤悉毕具。无一之或遗。俨乎乔梓相接。罍爵相望。莼城氏之本支昭穆。瞭然于一开卷。噫。勤哉。此孝子慈孙之所用心。而风树之感。羹墙之慕。豺獭之报。悉寓于其中。可谓文献足而有足徵者矣。槩以评之。监务公之心存旧国。命题前衔。罔仆自靖之志也。湖隐公之不慑刑祸。独守丧制。素冠棘栾之行也。朝奉公之好义喜施。祝半州之粥药乎。节度公之名武行儒。却中军之诗书乎。若夫凌虚先生。尤有大焉。就正有道。得闻大方。蔚为冥途指南。而西溪公又能趾美承烈。种学绩文。遵父师而启似续。则允矣先生之孙也。然则国祯之必以是名名是编者。其意岂不以不克负荷析薪忝矣。不肯堂搆塈茨忝矣。不勤服穑敷菑忝矣。不善箕裘弓冶忝矣乎。请演诗义而申勉焉。夫无忝由于勉学。勉学由于教善。教善由于畏天。畏天由于念先。是故。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所以念先也。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所以畏天也。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所以教善也。我日斯迈。尔月斯征。所以勉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8H 页
 学也。之四者不过曰孝敬慈友。为物之则民之彝。而孝源于百行。敬干于万事。无忝之道。于是焉备矣。虽然。其要惟在勉学。学非谓摛藻缀华。决科第。取功名。心读书以穷理。修身以俟命。以尽吾受中之责云尔。是乌待他求哉。国祯日与宗党子弟。取凌虚先生西溪公之所尝讲问资益于平日师友者。切磋琢磨。有如诗人之夙兴夜寐临深履薄之为。则溯而追之。沿而求之。又旁推而寻之。凡诸先世之忠孝节烈。德业行义。无不左右逢其原。晦翁所以语司马家子孙。必称公家文正。亦以是也。然则是录也。将为莼城氏之一部掌故。而东南文献之传。国祯家当偻其拇矣。安知异日。不有观礼者来徵而必曰有宋存焉。如夫子所云。国祯之功。于是为大。而晋阳有焰焰而起者。必莼城氏后与。间尝窃取佔𠌫先生明发窝故事。略有所撰次。而未及就绪。今玩国祯是录。尤有所起余者。遂书此归之。亦因以自勖。
学也。之四者不过曰孝敬慈友。为物之则民之彝。而孝源于百行。敬干于万事。无忝之道。于是焉备矣。虽然。其要惟在勉学。学非谓摛藻缀华。决科第。取功名。心读书以穷理。修身以俟命。以尽吾受中之责云尔。是乌待他求哉。国祯日与宗党子弟。取凌虚先生西溪公之所尝讲问资益于平日师友者。切磋琢磨。有如诗人之夙兴夜寐临深履薄之为。则溯而追之。沿而求之。又旁推而寻之。凡诸先世之忠孝节烈。德业行义。无不左右逢其原。晦翁所以语司马家子孙。必称公家文正。亦以是也。然则是录也。将为莼城氏之一部掌故。而东南文献之传。国祯家当偻其拇矣。安知异日。不有观礼者来徵而必曰有宋存焉。如夫子所云。国祯之功。于是为大。而晋阳有焰焰而起者。必莼城氏后与。间尝窃取佔𠌫先生明发窝故事。略有所撰次。而未及就绪。今玩国祯是录。尤有所起余者。遂书此归之。亦因以自勖。东儒心画序
凡物之有声色臭味者。人莫不嗜好而求畜之。为其适于吾之耳目鼻口也。至若古人之墨艺笔法。非有声色臭味之可以适于吾。而犹有嗜而好好而求者。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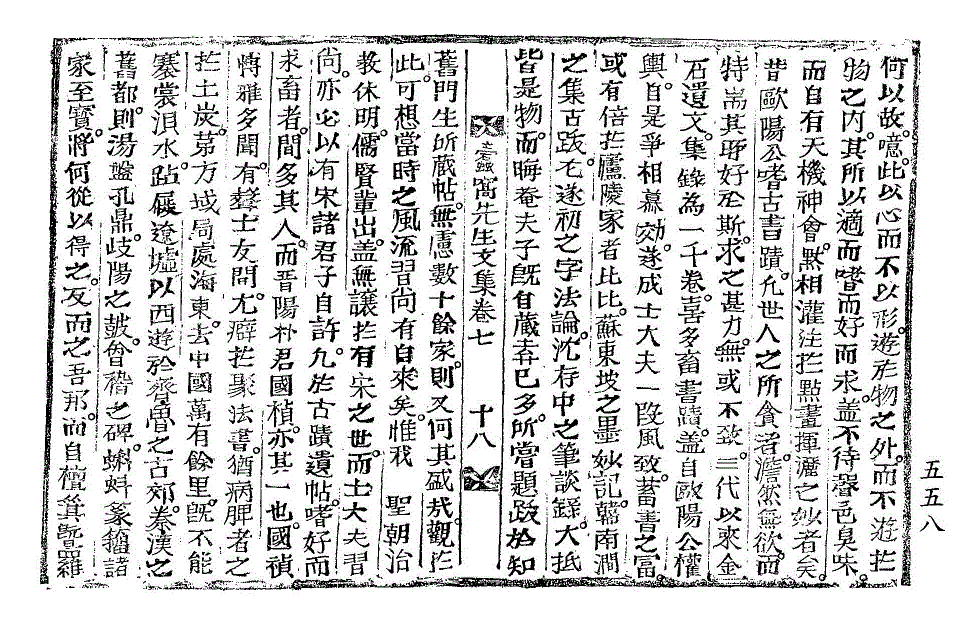 何以故。噫。此以心而不以形。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其所以适而嗜而好而求。盖不待声色臭味。而自有天机神会。默相灌注于点画挥洒之妙者矣。昔欧阳公嗜古书迹。凡世人之所贪者。澹然无欲。而特耑其所好于斯。求之甚力。无或不致。三代以来金石遗文。集录为一千卷。喜多畜书迹。盖自欧阳公权舆。自是争相慕效。遂成士大夫一段风致。蓄书之富。或有倍于庐陵家者比比。苏东坡之墨妙记。韩南涧之集古跋。尤遂初之字法论。沈存中之笔谈录。大抵皆是物。而晦庵夫子既自藏弆已多。所尝题跋于知旧门生所藏帖。无虑数十馀家。则又何其盛哉。观于此。可想当时之风流习尚有自来矣。惟我 圣朝治教休明。儒贤辈出。盖无让于有宋之世。而士大夫习尚。亦必以有宋诸君子自许。凡于古迹遗帖。嗜好而求畜者。间多其人。而晋阳朴君国祯。亦其一也。国祯。博雅多闻。有声士友间。尤癖于聚法书。犹病脾者之于土炭。第方域局处海东。去中国万有馀里。既不能褰裳浿水。跕屣辽墟以西游于齐,鲁之古郊。秦,汉之旧都。则汤盘孔鼎。岐阳之鼓。会稽之碑。蝌蚪篆籀诸家至宝。将何从以得之。反而之吾邦。而自檀箕暨罗
何以故。噫。此以心而不以形。游于物之外。而不游于物之内。其所以适而嗜而好而求。盖不待声色臭味。而自有天机神会。默相灌注于点画挥洒之妙者矣。昔欧阳公嗜古书迹。凡世人之所贪者。澹然无欲。而特耑其所好于斯。求之甚力。无或不致。三代以来金石遗文。集录为一千卷。喜多畜书迹。盖自欧阳公权舆。自是争相慕效。遂成士大夫一段风致。蓄书之富。或有倍于庐陵家者比比。苏东坡之墨妙记。韩南涧之集古跋。尤遂初之字法论。沈存中之笔谈录。大抵皆是物。而晦庵夫子既自藏弆已多。所尝题跋于知旧门生所藏帖。无虑数十馀家。则又何其盛哉。观于此。可想当时之风流习尚有自来矣。惟我 圣朝治教休明。儒贤辈出。盖无让于有宋之世。而士大夫习尚。亦必以有宋诸君子自许。凡于古迹遗帖。嗜好而求畜者。间多其人。而晋阳朴君国祯。亦其一也。国祯。博雅多闻。有声士友间。尤癖于聚法书。犹病脾者之于土炭。第方域局处海东。去中国万有馀里。既不能褰裳浿水。跕屣辽墟以西游于齐,鲁之古郊。秦,汉之旧都。则汤盘孔鼎。岐阳之鼓。会稽之碑。蝌蚪篆籀诸家至宝。将何从以得之。反而之吾邦。而自檀箕暨罗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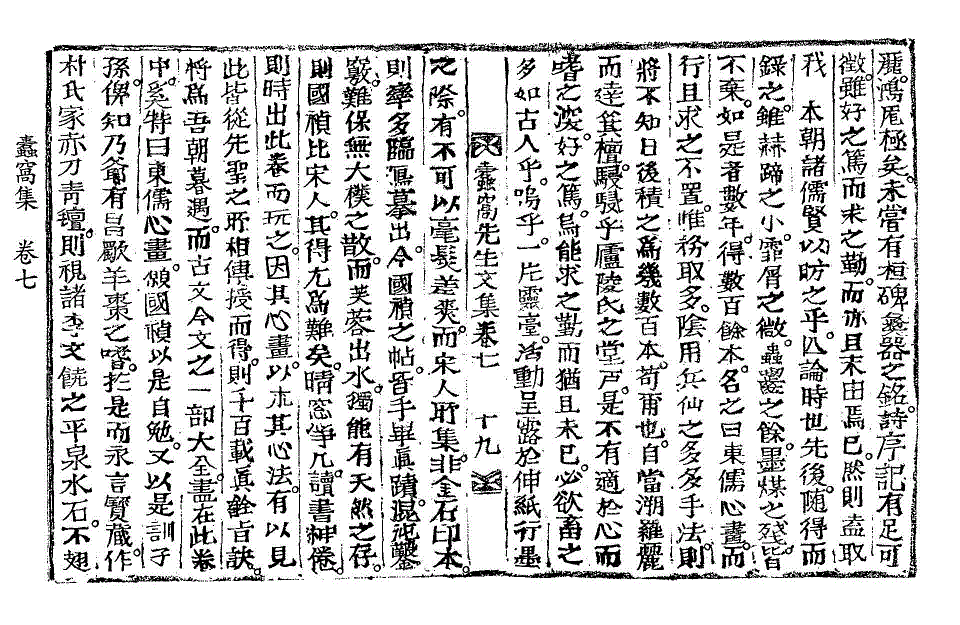 丽。鸿厖极矣。未尝有桓碑彝器之铭。诗序记有足可徵。虽好之笃而求之勤。而亦且末由焉已。然则盍取我 本朝诸儒贤以昉之乎。亡论时世先后。随得而录之。虽赫蹄之小。霏屑之微。虫齧之馀。墨煤之残。皆不弃。如是者数年。得数百馀本。名之曰东儒心画。而行且求之不置。惟务取多。阴用兵仙之多多手法。则将不知日后积之为几数百本。苟尔也。自当溯罗丽而达箕檀。骎骎乎庐陵氏之堂户。是不有适于心而嗜之深。好之笃。乌能求之勤而犹且未已。必欲畜之多如古人乎。呜乎。一片灵台。活动呈露于伸纸行墨之际。有不可以毫发差爽。而宋人所集。非金石印本。则率多临写摹出。今国祯之帖。皆手毕真迹。混沌凿窍。难保无大朴之散。而芙蓉出水。独能有天然之存。则国祯比宋人。其得尤为难矣。晴窗净几。读书神倦。则时出此卷而玩之。因其心画。以求其心法。有以见此皆从先圣之所相传授而得。则千百载真铨旨诀。将为吾朝暮遇。而古文今文之一部大全。尽在此卷中。奚特曰东儒心画。愿国祯以是自勉。又以是训子孙。俾知乃爷有昌歜羊枣之嗜。于是而永言宝藏。作朴氏家赤刀青毡。则视诸李文饶之平泉水石。不翅
丽。鸿厖极矣。未尝有桓碑彝器之铭。诗序记有足可徵。虽好之笃而求之勤。而亦且末由焉已。然则盍取我 本朝诸儒贤以昉之乎。亡论时世先后。随得而录之。虽赫蹄之小。霏屑之微。虫齧之馀。墨煤之残。皆不弃。如是者数年。得数百馀本。名之曰东儒心画。而行且求之不置。惟务取多。阴用兵仙之多多手法。则将不知日后积之为几数百本。苟尔也。自当溯罗丽而达箕檀。骎骎乎庐陵氏之堂户。是不有适于心而嗜之深。好之笃。乌能求之勤而犹且未已。必欲畜之多如古人乎。呜乎。一片灵台。活动呈露于伸纸行墨之际。有不可以毫发差爽。而宋人所集。非金石印本。则率多临写摹出。今国祯之帖。皆手毕真迹。混沌凿窍。难保无大朴之散。而芙蓉出水。独能有天然之存。则国祯比宋人。其得尤为难矣。晴窗净几。读书神倦。则时出此卷而玩之。因其心画。以求其心法。有以见此皆从先圣之所相传授而得。则千百载真铨旨诀。将为吾朝暮遇。而古文今文之一部大全。尽在此卷中。奚特曰东儒心画。愿国祯以是自勉。又以是训子孙。俾知乃爷有昌歜羊枣之嗜。于是而永言宝藏。作朴氏家赤刀青毡。则视诸李文饶之平泉水石。不翅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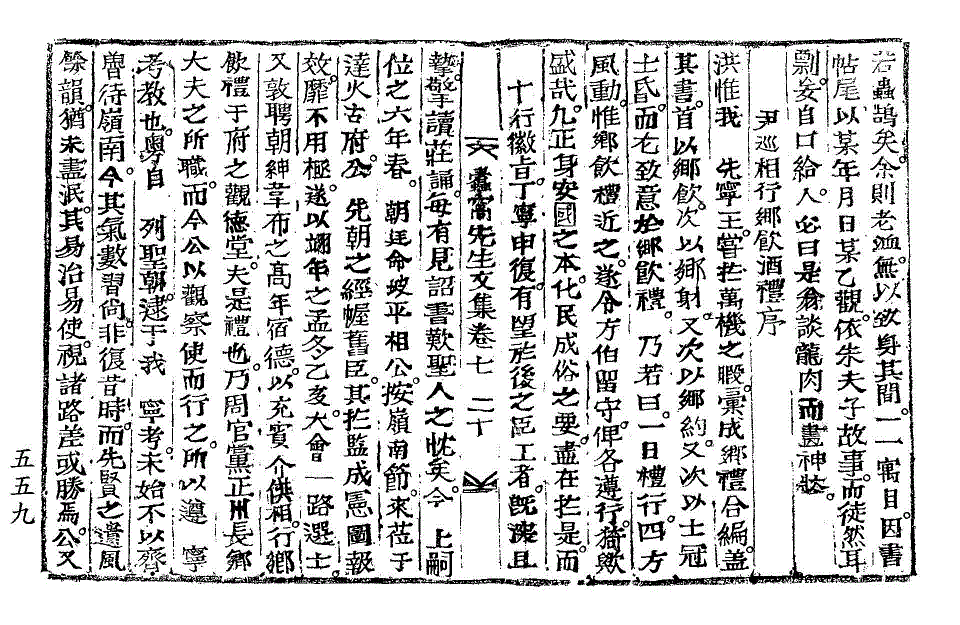 若虫鹄矣。余则老洫。无以致身其间。一一寓目。因书帖尾以某年月日某乙观。依朱夫子故事。而徒然耳剽。妄自口给。人必曰是翁谈龙肉而画神状。
若虫鹄矣。余则老洫。无以致身其间。一一寓目。因书帖尾以某年月日某乙观。依朱夫子故事。而徒然耳剽。妄自口给。人必曰是翁谈龙肉而画神状。尹巡相行乡饮酒礼序
洪惟我 先宁王。尝于万机之暇。汇成乡礼合编。盖其书。首以乡饮。次以乡射。又次以乡约。又次以士冠士昏。而尤致意于乡饮礼。 乃若曰。一日礼行。四方风动。惟乡饮礼近之。遂令方伯留守。俾各遵行。猗欤盛哉。凡正身安国之本。化民成俗之要。尽在于是。而 十行徽旨。丁宁申复。有望于后之臣工者。既深且挚。擎读庄诵。每有见诏书叹圣人之忱矣。今 上嗣位之六年春。 朝廷命坡平相公。按岭南节。来莅于达火古府。公 先朝之经幄旧臣。其于监成宪图报效。靡不用极。遂以翊年之孟冬乙亥。大会一路选士。又敦聘朝绅韦布之高年宿德。以充宾介僎相。行乡饮礼于府之观德堂。夫是礼也。乃周官党正州长乡大夫之所职。而今公以观察使而行之。所以遵 宁考教也。粤自 列圣朝。逮于我 宁考。未始不以齐,鲁待岭南。今其气数习尚。非复昔时。而先贤之遗风馀韵。犹未尽泯。其易治易使。视诸路差或胜焉。公又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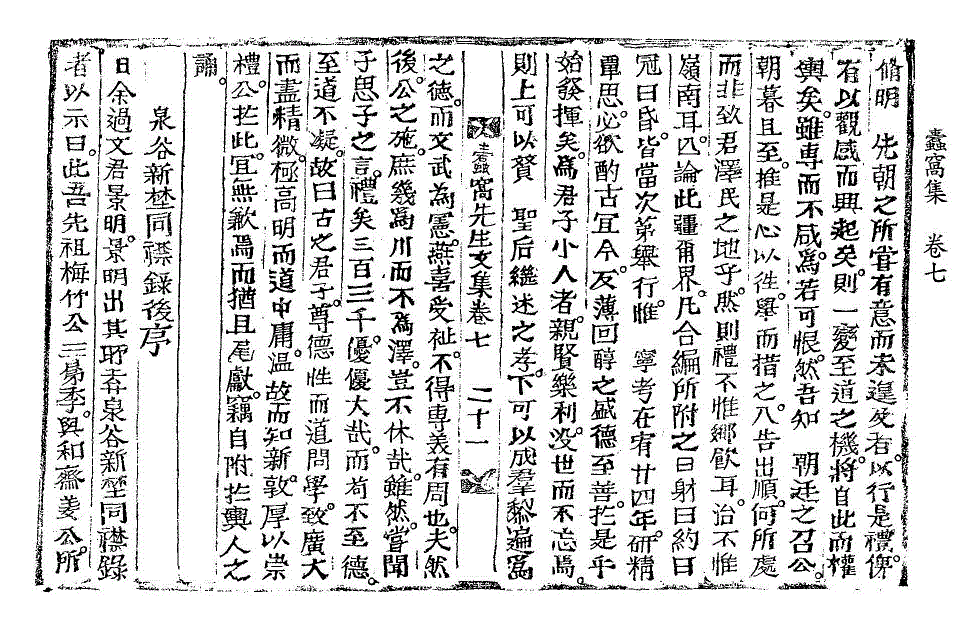 脩明 先朝之所尝有意而未遑及者。以行是礼。俾有以观感而兴起矣。则一变至道之机。将自此而权舆矣。虽专而不咸。为若可恨。然吾知 朝廷之召公。朝暮且至。推是心以往。举而措之。入告出顺。何所处而非致君泽民之地乎。然则礼不惟乡饮耳。治不惟岭南耳。亡论此疆尔界。凡合编所附之曰射曰约曰冠曰昏。皆当次第举行。惟 宁考在宥廿四年。研精覃思。必欲酌古宜今。反薄回醇之盛德至善。于是乎始发挥矣。为君子小人者。亲贤乐利。没世而不忘焉。则上可以赞 圣后继述之孝。下可以成群黎遍为之德。而文武为宪。燕喜受祉。不得专美有周也。夫然后。公之施。庶几为川而不为泽。岂不休哉。虽然。尝闻子思子之言。礼矣三百三千。优优大哉。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曰古之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公于此。宜无歉焉而犹且尾献。窃自附于舆人之诵。
脩明 先朝之所尝有意而未遑及者。以行是礼。俾有以观感而兴起矣。则一变至道之机。将自此而权舆矣。虽专而不咸。为若可恨。然吾知 朝廷之召公。朝暮且至。推是心以往。举而措之。入告出顺。何所处而非致君泽民之地乎。然则礼不惟乡饮耳。治不惟岭南耳。亡论此疆尔界。凡合编所附之曰射曰约曰冠曰昏。皆当次第举行。惟 宁考在宥廿四年。研精覃思。必欲酌古宜今。反薄回醇之盛德至善。于是乎始发挥矣。为君子小人者。亲贤乐利。没世而不忘焉。则上可以赞 圣后继述之孝。下可以成群黎遍为之德。而文武为宪。燕喜受祉。不得专美有周也。夫然后。公之施。庶几为川而不为泽。岂不休哉。虽然。尝闻子思子之言。礼矣三百三千。优优大哉。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曰古之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公于此。宜无歉焉而犹且尾献。窃自附于舆人之诵。泉谷新野同襟录后序
日余过文君景明。景明出其所弆泉谷新野同襟录者以示曰。此吾先祖梅竹公三昆季。与和斋姜公。所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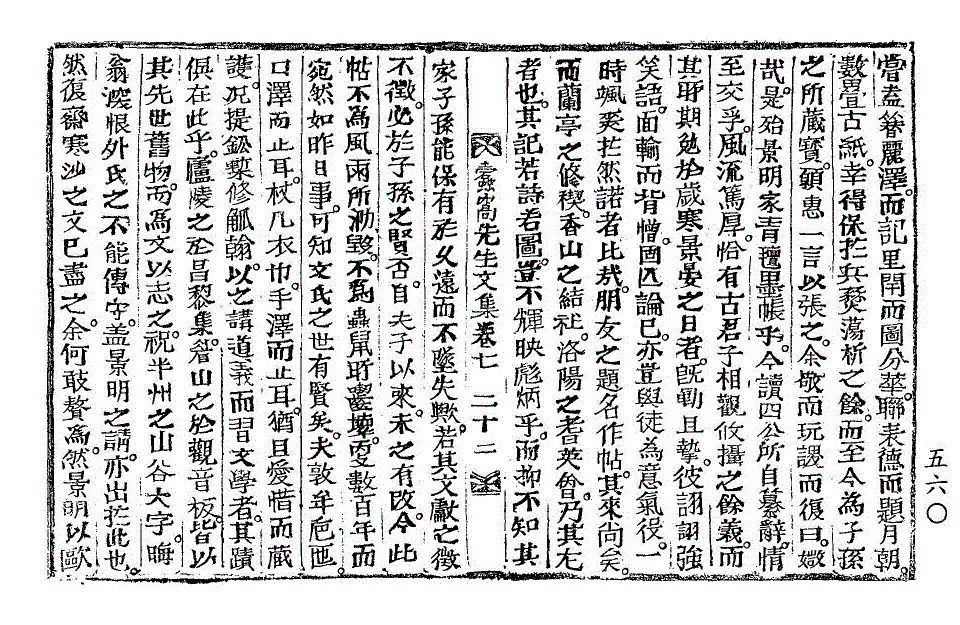 尝盍簪丽泽。而记里闬而图分华。联表德而题月朝。数叠古纸。幸得保于兵燹荡析之馀。而至今为子孙之所藏宝。愿惠一言以张之。余敬而玩谡而复曰。美哉。是殆景明家青毡墨帐乎。今读四公所自纂辞。情至交孚。风流笃厚。恰有古君子相观攸摄之馀义。而其所期勉于岁寒景晏之日者。既勤且挚。彼诩诩强笑语。面输而背憎。固亡论已。亦岂与徒为意气役。一时飒爽于然诺者比哉。朋友之题名作帖。其来尚矣。而兰亭之修稧。香山之结社。洛阳之耆英会。乃其尤者也。其记若诗若图。岂不辉映彪炳乎。而抑不知其家子孙能保有于久远而不坠失欤。若其文献之徵不徵。必于子孙之贤否。自夫子以来。未之有改。今此帖不为风雨所泐毁。不为虫鼠所齧坏。更数百年而宛然如昨日事。可知文氏之世有贤矣。夫敦牟卮匜。口泽而止耳。杖几衣巾。手泽而止耳。犹且爱惜而藏护。况提铅椠修觚翰。以之讲道义而习文学者。其迹俱在此乎。庐陵之于昌黎集。眉山之于观音板。皆以其先世旧物。而为文以志之。祝半州之山谷大字。晦翁深恨外氏之不能传守。盖景明之请。亦出于此也。然复斋寒沙之文已尽之。余何敢赘为。然景明以欧
尝盍簪丽泽。而记里闬而图分华。联表德而题月朝。数叠古纸。幸得保于兵燹荡析之馀。而至今为子孙之所藏宝。愿惠一言以张之。余敬而玩谡而复曰。美哉。是殆景明家青毡墨帐乎。今读四公所自纂辞。情至交孚。风流笃厚。恰有古君子相观攸摄之馀义。而其所期勉于岁寒景晏之日者。既勤且挚。彼诩诩强笑语。面输而背憎。固亡论已。亦岂与徒为意气役。一时飒爽于然诺者比哉。朋友之题名作帖。其来尚矣。而兰亭之修稧。香山之结社。洛阳之耆英会。乃其尤者也。其记若诗若图。岂不辉映彪炳乎。而抑不知其家子孙能保有于久远而不坠失欤。若其文献之徵不徵。必于子孙之贤否。自夫子以来。未之有改。今此帖不为风雨所泐毁。不为虫鼠所齧坏。更数百年而宛然如昨日事。可知文氏之世有贤矣。夫敦牟卮匜。口泽而止耳。杖几衣巾。手泽而止耳。犹且爱惜而藏护。况提铅椠修觚翰。以之讲道义而习文学者。其迹俱在此乎。庐陵之于昌黎集。眉山之于观音板。皆以其先世旧物。而为文以志之。祝半州之山谷大字。晦翁深恨外氏之不能传守。盖景明之请。亦出于此也。然复斋寒沙之文已尽之。余何敢赘为。然景明以欧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1H 页
 苏氏为法。以祝氏为戒。则其为保家主庶几夫。韩宣子曰。愿封植嘉树。以无忘角弓诗。请以此为景明勖。
苏氏为法。以祝氏为戒。则其为保家主庶几夫。韩宣子曰。愿封植嘉树。以无忘角弓诗。请以此为景明勖。邵城联芳集序
吾乡昔有松潭蔡公先生。乃陶山之横出一支也。既成进士。去而筑小有,狎鹭二亭于琴湖上王屋山下。隐居求志。教诸子。严有法度。诸子皆彬彬有文行。而琴滩,两传二公最贤。即西山家里伯静,仲默乎。盖琴滩公。尝游寒冈,旅轩,乐斋诸先生门。得闻为己之方。终始笃实。此慕堂孙公云。两传公。早有求道之志。初从芝山先生学。晚又事寒冈先生。卒以文学闻。此李公鸣宇云。皆洿不至阿其所好矣。龙蛇乱。先亭二所。熸于兵燹。其地为他人有。琴滩公归其直而重葺之。日与群弟讲学其中。一时诸名胜。无不来礼。而愚伏先生。亦以方伯屡倾盖焉。当昏朝时。李尔瞻用事。俶扰天纪。至有 西宫之变。而士皆噎喑媕婀。不敢出一言。两传公。倡起多士。上疏请斩。直声动一国。及其报罢而归。则谢绝公车。无复当世之志矣。噫美哉。难兄而难弟也。自夫二公歾后。行且数百馀年。而风流儒雅。尚在人牙颊。凡过小有,狎鹭之墟者。孰不想像谁昔。指点而赍咨。而第恨夫平生咳唾散落于人间。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1L 页
 直是一毫芒耳。蔡氏诸君。慨然于斯。旁搜曲访。各得诗若文若干篇。将欲付剞劂氏以寿其传。属余斤正。余谂之曰。今此篇什不赢。盍编为同集。不观夫松桂并社则益辣。兰蕙共亩则愈馨乎。咸曰诺。遂连比二稿。汇成一帙。合而目之曰邵城联芳集。盖记荀里表贾碑之义也。呜呼。今以二公幽閒之芳躅。脩洁之芳掺。集而联缀于一部编中。有如棣萼相辉。荆华交映。而幽香远臭。郁郁而斐亹焉。则当日之高行直节。于是乎不寂寥矣。后之观者。必将有挹遗芬而知钦。袭馀薰而思效。油然兴起于百世之下。况诸君抱昌歜之怀。发嘉树之思者。尤当如何也。然则是集也。虽其文辞略绰。而有补于世教。岂其微哉。介余往复者。琴滩公后必勋。两传公后允复。
直是一毫芒耳。蔡氏诸君。慨然于斯。旁搜曲访。各得诗若文若干篇。将欲付剞劂氏以寿其传。属余斤正。余谂之曰。今此篇什不赢。盍编为同集。不观夫松桂并社则益辣。兰蕙共亩则愈馨乎。咸曰诺。遂连比二稿。汇成一帙。合而目之曰邵城联芳集。盖记荀里表贾碑之义也。呜呼。今以二公幽閒之芳躅。脩洁之芳掺。集而联缀于一部编中。有如棣萼相辉。荆华交映。而幽香远臭。郁郁而斐亹焉。则当日之高行直节。于是乎不寂寥矣。后之观者。必将有挹遗芬而知钦。袭馀薰而思效。油然兴起于百世之下。况诸君抱昌歜之怀。发嘉树之思者。尤当如何也。然则是集也。虽其文辞略绰。而有补于世教。岂其微哉。介余往复者。琴滩公后必勋。两传公后允复。琴滩文集序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世之尚论之士。以是为口实。然其意。盖曰古与今辽夐矣。所可放信。惟在于籍。是二者而阶之云尔。岂直谓雕缋以为工。覼缕以为多。如后世之为然后。乃可以知其人哉。夫君子贵实行而贱文辞尚矣。立言居德功之次。游艺处据依之末。其人苟可也。在外之糠秕糟粕。有不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2H 页
 可论。否则虽多且工。特木华耳。鸟音耳。本之则无。何取焉。日蔡君德尧。赍其先祖琴滩公遗稿及师门札翰。诸名胜题咏。来属余雠校。且徵以弁文。余固非其人。顾以乡里后生。有不可终辞者。谨受而卒业。盖诗八,书问目一,祝文三。噫。甚矣其寂寥哉。后公数百馀年。而欲论公之世。不几为描空而画神乎。然公以松潭先生子夙有所擩染于家庭。而出而从寒冈,旅轩,乐斋诸先生。游。焄炙而观感者。盖亦多矣。是故。其见于文辞。虽微矣。端序则具。疑文变节。质之师门。所以惕于沽礼也。深慕至恫。著之侑辞。所以笃于明发也。至若重葺先亭。与弟酬唱。其惟勤肯搆而乐湛和乎。寄赠乡友。谋酒招邀。其惟耻市道而敦世好乎。及夫壬戌秋七。与客登舟。沿洄上下。水月无尽。则襟韵飘洒。尘累融涤。恍若揖苏仙于千载而问赤壁之清游矣。即此数篇。亦足以想像公平生之一二。而拾炉零金。不害为宝。尝鼎片脔。犹觉为珍。何必多乎哉。况当时之行过东西州者。亡论冠盖簦屩。率造其庐而题其亭。风流文采。照映湖山。昌黎公所谓观其所与之多寡者。不虚语也。又按诸贤为公呈褒曰。出入函席。学知为己。终始笃实。一乡推重。于是乎益知公所存。
可论。否则虽多且工。特木华耳。鸟音耳。本之则无。何取焉。日蔡君德尧。赍其先祖琴滩公遗稿及师门札翰。诸名胜题咏。来属余雠校。且徵以弁文。余固非其人。顾以乡里后生。有不可终辞者。谨受而卒业。盖诗八,书问目一,祝文三。噫。甚矣其寂寥哉。后公数百馀年。而欲论公之世。不几为描空而画神乎。然公以松潭先生子夙有所擩染于家庭。而出而从寒冈,旅轩,乐斋诸先生。游。焄炙而观感者。盖亦多矣。是故。其见于文辞。虽微矣。端序则具。疑文变节。质之师门。所以惕于沽礼也。深慕至恫。著之侑辞。所以笃于明发也。至若重葺先亭。与弟酬唱。其惟勤肯搆而乐湛和乎。寄赠乡友。谋酒招邀。其惟耻市道而敦世好乎。及夫壬戌秋七。与客登舟。沿洄上下。水月无尽。则襟韵飘洒。尘累融涤。恍若揖苏仙于千载而问赤壁之清游矣。即此数篇。亦足以想像公平生之一二。而拾炉零金。不害为宝。尝鼎片脔。犹觉为珍。何必多乎哉。况当时之行过东西州者。亡论冠盖簦屩。率造其庐而题其亭。风流文采。照映湖山。昌黎公所谓观其所与之多寡者。不虚语也。又按诸贤为公呈褒曰。出入函席。学知为己。终始笃实。一乡推重。于是乎益知公所存。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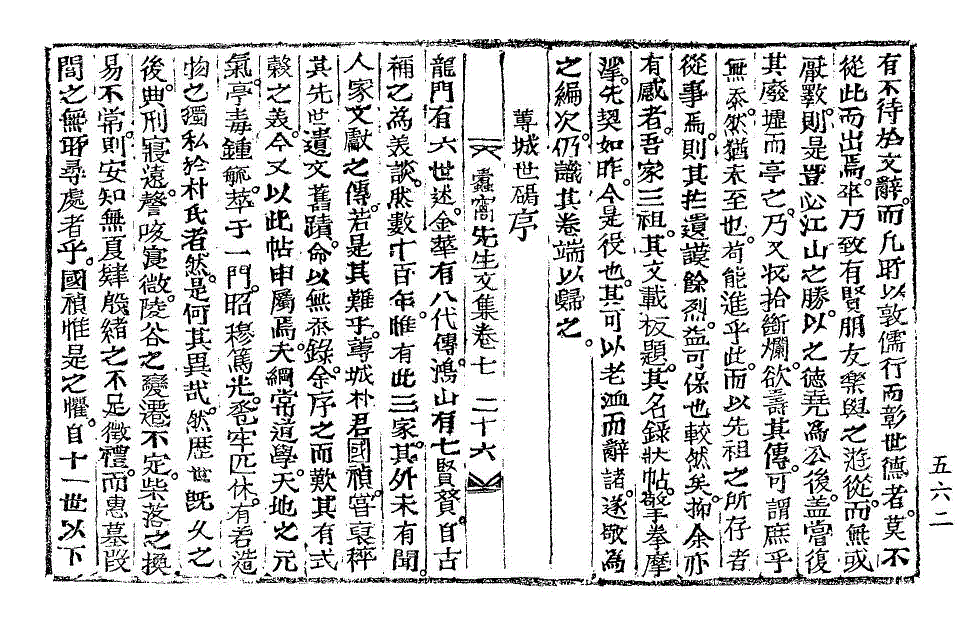 有不待于文辞。而凡所以敦儒行而彰世德者。莫不从此而出焉。卒乃致有贤朋友乐与之游从。而无或厌斁。则是岂必江山之胜。以之德尧为公后。盖尝复其废墟而亭之。乃又收拾断烂。欲寿其传。可谓庶乎无忝。然犹未至也。苟能进乎此。而以先祖之所存者从事焉。则其于遗谟馀烈。益可保也较然矣。抑余亦有感者。吾家三祖。其文载板题。其名录状帖。擎拳摩挲。先契如昨。今是役也。其可以老洫而辞诸。遂敬为之编次。仍识其卷端以归之。
有不待于文辞。而凡所以敦儒行而彰世德者。莫不从此而出焉。卒乃致有贤朋友乐与之游从。而无或厌斁。则是岂必江山之胜。以之德尧为公后。盖尝复其废墟而亭之。乃又收拾断烂。欲寿其传。可谓庶乎无忝。然犹未至也。苟能进乎此。而以先祖之所存者从事焉。则其于遗谟馀烈。益可保也较然矣。抑余亦有感者。吾家三祖。其文载板题。其名录状帖。擎拳摩挲。先契如昨。今是役也。其可以老洫而辞诸。遂敬为之编次。仍识其卷端以归之。莼城世碣序
龙门有六世述。金华有八代传。鸿山有七贤赞。自古称之为美谈。然数十百年。惟有此三家。其外未有闻。人家文献之传。若是其难乎。莼城朴君国祯。尝裒稡其先世遗文旧迹。命以无忝录。余序之而叹其有式谷之美。今又以此帖申属焉。夫纲常道学。天地之元气。亭毒钟毓。萃于一门。昭穆笃光。卺牢匹休。有若造物之独私于朴氏者然。是何其异哉。然历世既久之后。典刑寝远。謦咳寖微。陵谷之变迁不定。柴落之换易不常。则安知无夏肄殷绪之不足徵礼。而惠墓段闾之无所寻处者乎。国祯惟是之惧。自十一世以下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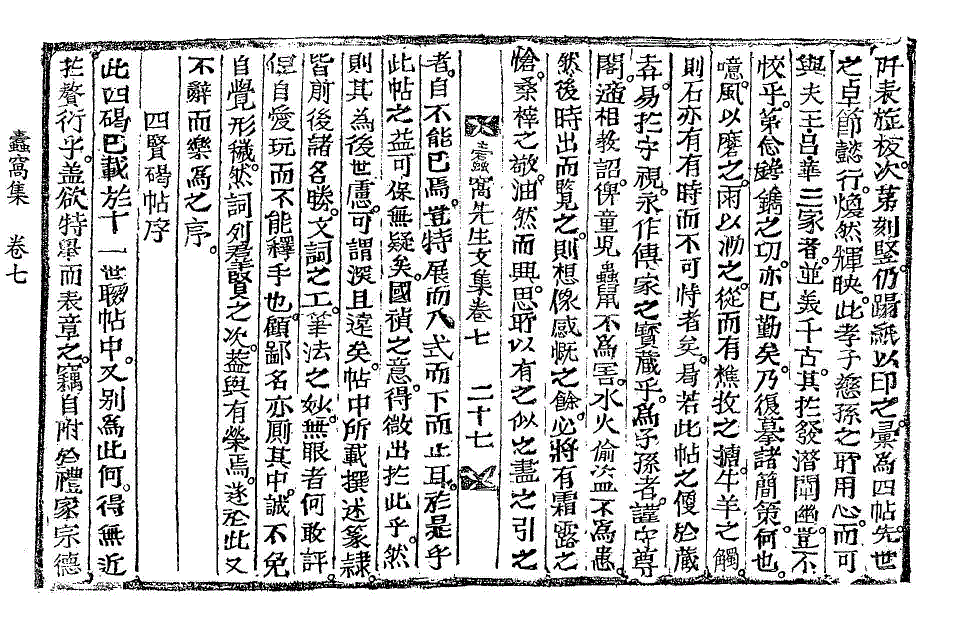 阡表㫌板。次第刻竖。仍蹋纸以印之。汇为四帖。先世之卓节懿行。焕然辉映。此孝子慈孙之所用心。而可与夫王,吕,华三家者。并美千古。其于发潜阐幽。岂不恔乎。第念镵镌之功。亦已勤矣。乃复摹诸简策。何也。噫。风以磨之。雨以泐之。从而有樵牧之搪。牛羊之触。则石亦有有时而不可恃者矣。曷若此帖之便于藏弆。易于守视。永作传家之宝藏乎。为子孙者。谨守尊阁。遆相教诏。俾童儿虫鼠不为害。水火偷盗不为患。然后时出而览之。则想像感慨之馀。必将有霜露之怆。桑梓之敬。油然而兴。思所以有之似之尽之引之者。自不能已焉。岂特展而入式而下而止耳。于是乎此帖之益可保无疑矣。国祯之意。得微出于此乎。然则其为后世虑。可谓深且远矣。帖中所载撰述篆隶。皆前后诸名胜。文词之工。笔法之妙。无眼者何敢评。但自爱玩而不能释手也。顾鄙名亦厕其中。诚不免自觉形秽。然词列群贤之次。盖与有荣焉。遂于此又不辞而乐为之序。
阡表㫌板。次第刻竖。仍蹋纸以印之。汇为四帖。先世之卓节懿行。焕然辉映。此孝子慈孙之所用心。而可与夫王,吕,华三家者。并美千古。其于发潜阐幽。岂不恔乎。第念镵镌之功。亦已勤矣。乃复摹诸简策。何也。噫。风以磨之。雨以泐之。从而有樵牧之搪。牛羊之触。则石亦有有时而不可恃者矣。曷若此帖之便于藏弆。易于守视。永作传家之宝藏乎。为子孙者。谨守尊阁。遆相教诏。俾童儿虫鼠不为害。水火偷盗不为患。然后时出而览之。则想像感慨之馀。必将有霜露之怆。桑梓之敬。油然而兴。思所以有之似之尽之引之者。自不能已焉。岂特展而入式而下而止耳。于是乎此帖之益可保无疑矣。国祯之意。得微出于此乎。然则其为后世虑。可谓深且远矣。帖中所载撰述篆隶。皆前后诸名胜。文词之工。笔法之妙。无眼者何敢评。但自爱玩而不能释手也。顾鄙名亦厕其中。诚不免自觉形秽。然词列群贤之次。盖与有荣焉。遂于此又不辞而乐为之序。四贤碣帖序
此四碣已载于十一世联帖中。又别为此何。得无近于赘衍乎。盖欲特举而表章之。窃自附于礼家宗德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3L 页
 之馀义耳。湖隐公以孝。佐郎公以忠。凌虚,西溪二先生以道学。夫人之所以为人而最灵于万物者。以其有三者也。之三者。撑天地亘万古。不可一日而暂无。无是则人之理或几乎息矣。然环一世之广。历百年之久。而能以忠孝闻者。盖无多也。至于道学。尤寥寥焉。何其难哉。莼城氏自先奕世济美。皆可以称述。而惟此四贤。又蔚然相望于前后。其所树立而成就者。大为 国家之所㫌表。师友之所推许也。则纲纪伦常。以之而植矣。渊源心法。以之而传矣。夫以一之为难。而今乃四贤继起。三难并有。有如恒物之取诸其室中而用之。虽使百世之上。千里之外。苟有如此人者。犹且想像钦慕而不能已。而况为吾之祖而精神血脉之流通于吾者乎。必欲尊而异之。为永世准则。人情固也。是故。凡于先世。必取其最贤者。尤致意焉。自诗书以来。莫不皆然。奚独于此帖。必嫌其重复。吾知联四帖。所以阐先烈也。别一帖。所以启后教也。世之好古者。必曰禹篆,汤盘,周鼓,孔鼎。是岂不苍然奇且古。而适于嗜悦于玩而已。何预于我事。然则贻谟锡类。不待他求。可以得之于此矣。惟其曰孝曰忠曰道学。各以其所盛者而名之耳。非其理有二也。必先
之馀义耳。湖隐公以孝。佐郎公以忠。凌虚,西溪二先生以道学。夫人之所以为人而最灵于万物者。以其有三者也。之三者。撑天地亘万古。不可一日而暂无。无是则人之理或几乎息矣。然环一世之广。历百年之久。而能以忠孝闻者。盖无多也。至于道学。尤寥寥焉。何其难哉。莼城氏自先奕世济美。皆可以称述。而惟此四贤。又蔚然相望于前后。其所树立而成就者。大为 国家之所㫌表。师友之所推许也。则纲纪伦常。以之而植矣。渊源心法。以之而传矣。夫以一之为难。而今乃四贤继起。三难并有。有如恒物之取诸其室中而用之。虽使百世之上。千里之外。苟有如此人者。犹且想像钦慕而不能已。而况为吾之祖而精神血脉之流通于吾者乎。必欲尊而异之。为永世准则。人情固也。是故。凡于先世。必取其最贤者。尤致意焉。自诗书以来。莫不皆然。奚独于此帖。必嫌其重复。吾知联四帖。所以阐先烈也。别一帖。所以启后教也。世之好古者。必曰禹篆,汤盘,周鼓,孔鼎。是岂不苍然奇且古。而适于嗜悦于玩而已。何预于我事。然则贻谟锡类。不待他求。可以得之于此矣。惟其曰孝曰忠曰道学。各以其所盛者而名之耳。非其理有二也。必先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4H 页
 以道学为主以立其体。则发于用而为忠为孝。无所处而不当。夫然后庶乎其可欤。然之三者。乃宇宙间公物。子孙亦不得以私焉。异日者安知无闻风而兴起。徵礼而来观者乎。于是焉幸出而示之。则其有补于世教。亦不少矣。帖中附诸贤所记述题味。而眉叟先生手笔亦在焉。皆足以旁照而徵信。亦以并书。
以道学为主以立其体。则发于用而为忠为孝。无所处而不当。夫然后庶乎其可欤。然之三者。乃宇宙间公物。子孙亦不得以私焉。异日者安知无闻风而兴起。徵礼而来观者乎。于是焉幸出而示之。则其有补于世教。亦不少矣。帖中附诸贤所记述题味。而眉叟先生手笔亦在焉。皆足以旁照而徵信。亦以并书。渔隐遗稿序
余尝扫尘于西溪先生集中。得其所以教子孙者。书非圣贤。行非孝悌则不道也。虽以古之颜,吕氏家法。殆不加此。宜其后必多有彬彬者乎。及睹渔隐公遗稿信然。盖先生有二子。皆式谷而公其次子也。自少擩染惯习。娴于文学。驯于言行。既成进士。遂与伯氏公。杜门扫轨。养亲课儿以自乐。凡于势利纷华。泊然无所好。家故不贫。而未或以是为其所豢焉。及其晚年。生事旁落。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固如此。有时兴至。则辄扶筇蹑扉。放浪啸傲于云林泉石间。既而涉露梁登锦山。以望日出之海。既归而奚囊之腹。果然望矣。自号曰渔隐。所以志其志也。是故。其发于辞气者。皆从手分出。不暇乎藻缋篆刻。而恰有家学之典刑。诗则闲澹夷旷。涤腥荤闹热之气。文则平铺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4L 页
 纡馀。绝险苦艰涩之想。是固公之天得。而亦素所焄炙以之也。第恨夫以公之才之美。所经济者。花竹鱼鸟而止耳。所题品者。佛殿梵宇而止耳。则公之所不能者。天耶人耶。是未可知已。虽然。得人之所乐有。而又乐其所性而全之。彼在外之得不得。何足为公病。日。公之孙天东。赍是卷以来。徵文弁其端。辞之不获。则谨受而商之。诗若干文若干。而诗多于文十之七八。遂书此为渔隐遗稿序。
纡馀。绝险苦艰涩之想。是固公之天得。而亦素所焄炙以之也。第恨夫以公之才之美。所经济者。花竹鱼鸟而止耳。所题品者。佛殿梵宇而止耳。则公之所不能者。天耶人耶。是未可知已。虽然。得人之所乐有。而又乐其所性而全之。彼在外之得不得。何足为公病。日。公之孙天东。赍是卷以来。徵文弁其端。辞之不获。则谨受而商之。诗若干文若干。而诗多于文十之七八。遂书此为渔隐遗稿序。石浦子遗集序
余于自古文章。有韩公悲醉乡之意。盖不遇圣人以取栽焉。为甚不幸。至如时世之不遇。则有不暇论也。孔门四科。子贡,子游,子夏。以言语文学称。此有闻于夫子之文章而得之矣。当周之衰。奇邪诡异。甚于洪猛。之三子者。苟不及门而亲炙。几何不流而为仪,衍,庄,列归乎。而乃能终闻一贯。身通六艺。优入四科之列者。以其幸而遇夫子也。夫乐记,檀弓,礼运,大序等篇。是何等好文章。自是以后。文章遂病矣。惟汉唐宋最称为杰然。其间以文章名家者。可谓项背相望。然二三子外。皆少醇多疵。均之为春秋无义战。彼六朝也五季也。候虫时鸟之乍鸣乍息耳。置之无讥可也。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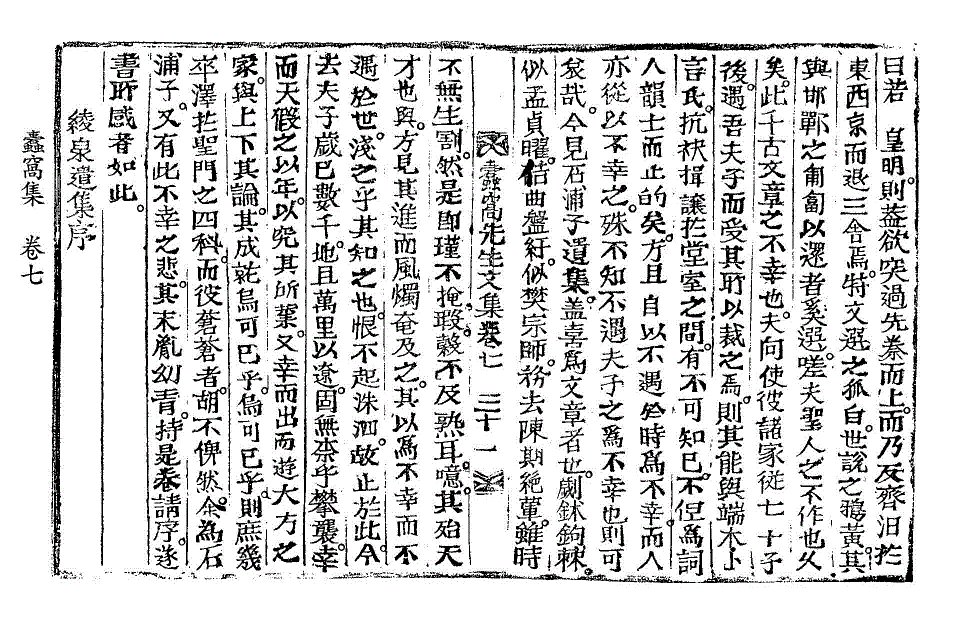 曰若 皇明。则盖欲突过先秦而上。而乃反齐汩于东西京而退三舍焉。特文选之狐白。世说之鸦黄。其与邯郸之匍匐以还者奚选。嗟夫圣人之不作也久矣。此千古文章之不幸也。夫向使彼诸家从七十子后。遇吾夫子而受其所以裁之焉。则其能与端木,卜,言氏。抗袂揖让于堂室之间。有不可知已。不但为词人韵士而止的矣。方且自以不遇于时为不幸。而人亦从以不幸之。殊不知不遇夫子之为不幸也则可哀哉。今见石浦子遗集。盖喜为文章者也。刿鉥钩棘。似孟贞曜。佶曲盘纡。似樊宗师。务去陈期绝荤。虽时不无生割。然是即瑾不掩瑕。谷不及熟耳。噫。其殆天才也与。方见其进而风烛奄及之。其以为不幸而不遇于世。浅之乎其知之也。恨不起洙泗。故止于此。今去夫子岁已数千。地且万里以辽。固无柰乎攀袭。幸而天假之以年。以究其所业。又幸而出而游大方之家。与上下其论。其成就乌可已乎。乌可已乎。则庶几卒泽于圣门之四科。而彼苍苍者。胡不俾然。余为石浦子。又有此不幸之悲。其末胤幼青。持是卷请序。遂书所感者如此。
曰若 皇明。则盖欲突过先秦而上。而乃反齐汩于东西京而退三舍焉。特文选之狐白。世说之鸦黄。其与邯郸之匍匐以还者奚选。嗟夫圣人之不作也久矣。此千古文章之不幸也。夫向使彼诸家从七十子后。遇吾夫子而受其所以裁之焉。则其能与端木,卜,言氏。抗袂揖让于堂室之间。有不可知已。不但为词人韵士而止的矣。方且自以不遇于时为不幸。而人亦从以不幸之。殊不知不遇夫子之为不幸也则可哀哉。今见石浦子遗集。盖喜为文章者也。刿鉥钩棘。似孟贞曜。佶曲盘纡。似樊宗师。务去陈期绝荤。虽时不无生割。然是即瑾不掩瑕。谷不及熟耳。噫。其殆天才也与。方见其进而风烛奄及之。其以为不幸而不遇于世。浅之乎其知之也。恨不起洙泗。故止于此。今去夫子岁已数千。地且万里以辽。固无柰乎攀袭。幸而天假之以年。以究其所业。又幸而出而游大方之家。与上下其论。其成就乌可已乎。乌可已乎。则庶几卒泽于圣门之四科。而彼苍苍者。胡不俾然。余为石浦子。又有此不幸之悲。其末胤幼青。持是卷请序。遂书所感者如此。绫泉遗集序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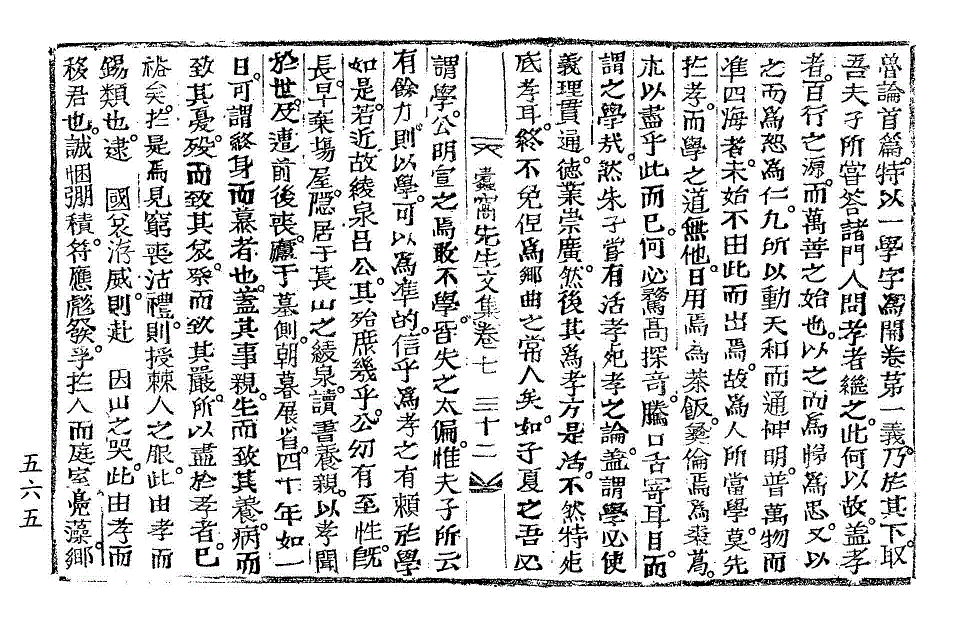 鲁论首篇。特以一学字为开卷第一义。乃于其下。取吾夫子所尝答诸门人问孝者继之。此何以故。盖孝者。百行之源。而万善之始也。以之而为悌为忠。又以之而为恕为仁。凡所以动天和而通神明。普万物而准四海者。未始不由此而出焉。故为人所当学。莫先于孝。而学之道无他。日用焉为茶饭。彝伦焉为裘葛。求以尽乎此而已。何必骛高探奇。腾口舌寄耳目。而谓之学哉。然朱子尝有活孝死孝之论。盖谓学必使义理贯通。德业崇广。然后其为孝方是活。不然特死底孝耳。终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矣。如子夏之吾必谓学。公明宣之焉敢不学。皆失之太偏。惟夫子所云有馀力。则以学。可以为准的。信乎为孝之有赖于学如是。若近故绫泉吕公。其殆庶几乎。公幼有至性。既长。早弃场屋。隐居于苌山之绫泉。读书养亲。以孝闻于世。及遭前后丧。庐于墓侧。朝暮展省。四十年如一日。可谓终身而慕者也。盖其事亲。生而致其养。病而致其忧。殁而致其哀。祭而致其严。所以尽于孝者。已裕矣。于是焉见穷丧沽礼。则授棘人之服。此由孝而锡类也。逮 国哀荐威。则赴 因山之哭。此由孝而移君也。诚悃弸积。符应彪发。孚于人而庭室凫藻。乡
鲁论首篇。特以一学字为开卷第一义。乃于其下。取吾夫子所尝答诸门人问孝者继之。此何以故。盖孝者。百行之源。而万善之始也。以之而为悌为忠。又以之而为恕为仁。凡所以动天和而通神明。普万物而准四海者。未始不由此而出焉。故为人所当学。莫先于孝。而学之道无他。日用焉为茶饭。彝伦焉为裘葛。求以尽乎此而已。何必骛高探奇。腾口舌寄耳目。而谓之学哉。然朱子尝有活孝死孝之论。盖谓学必使义理贯通。德业崇广。然后其为孝方是活。不然特死底孝耳。终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矣。如子夏之吾必谓学。公明宣之焉敢不学。皆失之太偏。惟夫子所云有馀力。则以学。可以为准的。信乎为孝之有赖于学如是。若近故绫泉吕公。其殆庶几乎。公幼有至性。既长。早弃场屋。隐居于苌山之绫泉。读书养亲。以孝闻于世。及遭前后丧。庐于墓侧。朝暮展省。四十年如一日。可谓终身而慕者也。盖其事亲。生而致其养。病而致其忧。殁而致其哀。祭而致其严。所以尽于孝者。已裕矣。于是焉见穷丧沽礼。则授棘人之服。此由孝而锡类也。逮 国哀荐威。则赴 因山之哭。此由孝而移君也。诚悃弸积。符应彪发。孚于人而庭室凫藻。乡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6H 页
 党薰陶。感于物而獐雉供羞。蝗螣效异。倘所谓至諴动神者。非欤。当是时。贤士大夫之之东西州者。或有造庐而礼之。或有登状而褒之。遗芬剩馥。至今使行路。想像感慨。指点而赍咨曰。此乃吕孝子之闾。是岂无所由而然乎。公甫离龀。受孝经小学而读之。犁然喜曰。童子之学。无过于此。公之孝。此其权舆矣。既而闻埙篪两郑先生讲学于横溪上。亟往从之。得闻绪论以归。终日端坐。讲其所闻。而尤味于洛建诸书。非甚病未尝或废。夷考其孝。不特生质之美以然。亦资之于学而有得焉。有不可诬也。日公之曾孙齐吉。赍遗藁一卷。以其再从父载扬甫书来。属以雠校。徵文弁其端。谨受而卒业焉。盖诗赋若杂文凡若干篇。万寿堂永慕斋诗及记。是惟白华之爱。南陔之养乎。亦惟小宛之怀。匪莪之痛乎。至若慎其独。求放心。何必曰利诸赋及山水吟,方塘记。皆能有以深发审机遏欲之徵义。默契观物养性之遗旨。而其他比兴叙述。亦莫不本于天理民彝之实。出于躬行心得之馀。则此可见公之学之所造。而非真为死孝者比审矣。昔余先君子。尝从公学。识公行事甚详。余自幼已耳稔而心盐之。既孤露。播越江西。一未能寻公绫泉旧居。
党薰陶。感于物而獐雉供羞。蝗螣效异。倘所谓至諴动神者。非欤。当是时。贤士大夫之之东西州者。或有造庐而礼之。或有登状而褒之。遗芬剩馥。至今使行路。想像感慨。指点而赍咨曰。此乃吕孝子之闾。是岂无所由而然乎。公甫离龀。受孝经小学而读之。犁然喜曰。童子之学。无过于此。公之孝。此其权舆矣。既而闻埙篪两郑先生讲学于横溪上。亟往从之。得闻绪论以归。终日端坐。讲其所闻。而尤味于洛建诸书。非甚病未尝或废。夷考其孝。不特生质之美以然。亦资之于学而有得焉。有不可诬也。日公之曾孙齐吉。赍遗藁一卷。以其再从父载扬甫书来。属以雠校。徵文弁其端。谨受而卒业焉。盖诗赋若杂文凡若干篇。万寿堂永慕斋诗及记。是惟白华之爱。南陔之养乎。亦惟小宛之怀。匪莪之痛乎。至若慎其独。求放心。何必曰利诸赋及山水吟,方塘记。皆能有以深发审机遏欲之徵义。默契观物养性之遗旨。而其他比兴叙述。亦莫不本于天理民彝之实。出于躬行心得之馀。则此可见公之学之所造。而非真为死孝者比审矣。昔余先君子。尝从公学。识公行事甚详。余自幼已耳稔而心盐之。既孤露。播越江西。一未能寻公绫泉旧居。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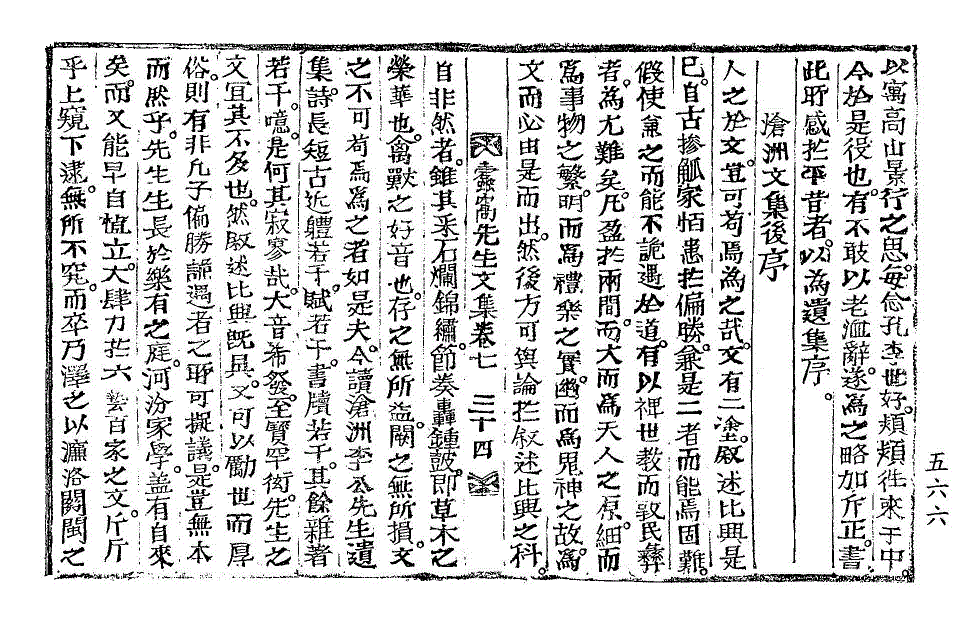 以寓高山景行之思。每念孔李世好。颎颎往来于中。今于是役也。有不敢以老洫辞。遂为之略加斥正。书此所感于平昔者。以为遗集序。
以寓高山景行之思。每念孔李世好。颎颎往来于中。今于是役也。有不敢以老洫辞。遂为之略加斥正。书此所感于平昔者。以为遗集序。沧洲文集后序
人之于文。岂可苟焉为之哉。文有二涂。叙述比兴是已。自古掺觚家恒患于偏胜。兼是二者而能焉固难。假使兼之而能不诡遇于道。有以裨世教而敦民彝者。为尤难矣。凡盈于两间。而大而为天人之原。细而为事物之繁。明而为礼乐之实。幽而为鬼神之故。为文而必由是而出。然后方可与论于叙述比兴之科。自非然者。虽其采石烂锦绣。节奏轰钟鼓。即草木之荣华也。禽兽之好音也。存之无所益。阙之无所损。文之不可苟焉为之者如是夫。今读沧洲李公先生遗集。诗长短古近体若干。赋若干。书牍若干。其馀杂著若干。噫。是何其寂寥哉。大音希发。至宝罕衒。先生之文宜其不多也。然叙述比兴既具。又可以励世而厚俗。则有非凡子偏胜诡遇者之所可拟议。是岂无本而然乎。先生生长于乐有之庭。河汾家学。盖有自来矣。而又能早自植立。大肆力于六艺百家之文。斤斤乎上窥下逮。无所不究。而卒乃泽之以濂洛关闽之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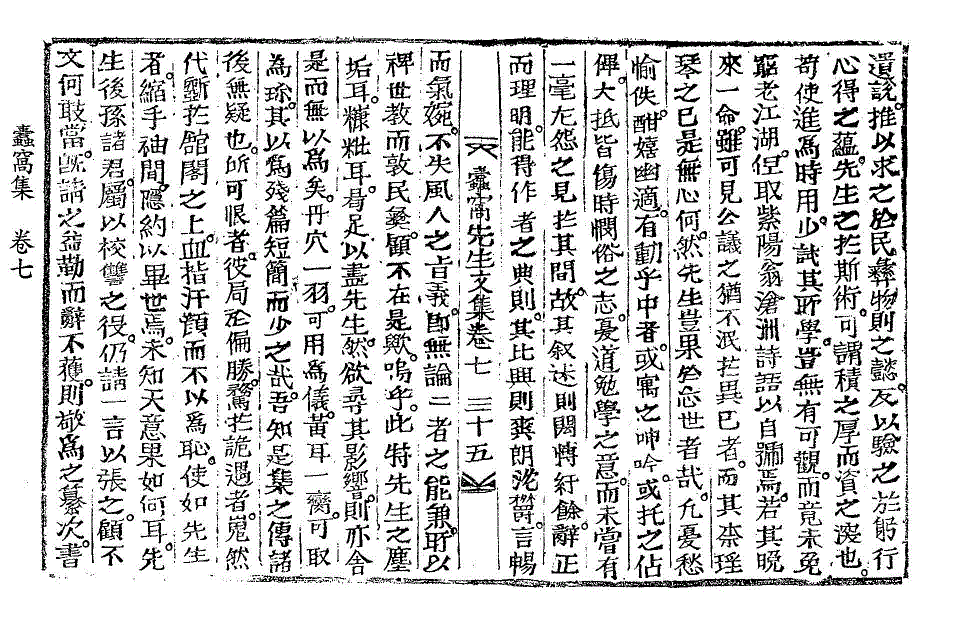 遗说。推以求之于民彝物则之懿。反以验之于躬行心得之蕴。先生之于斯术。可谓积之厚而资之深也。苟使进为时用。少试其所学。岂无有可观。而竟未免穷老江湖。但取紫阳翁沧洲诗语以自号焉。若其晚来一命。虽可见公议之犹不泯于异己者。而其柰瑶琴之已是无心何。然先生岂果于忘世者哉。凡忧愁愉佚。酣嬉幽适。有动乎中者。或寓之呻吟。或托之佔𠌫。大抵皆伤时悯俗之志。忧道勉学之意。而未尝有一毫尤怨之见于其间。故其叙述则闳博纡馀。辞正而理明。能得作者之典则。其比兴则爽朗沈郁。言畅而气婉。不失风人之旨义。即无论二者之能兼。所以裨世教而敦民彝。顾不在是欤。呜乎。此特先生之尘垢耳。糠秕耳。曷足以尽先生。然欲寻其影响。则亦舍是而无以为矣。丹穴一羽。可用为仪。黄耳一脔。可取为珍。其以为残篇短简而少之哉。吾知是集之传诸后无疑也。所可恨者。彼局于偏胜。骛于诡遇者。嵬然代斲于馆阁之上。血指汗颜而不以为耻。使如先生者。缩手袖间。隐约以毕世焉。未知天意果如何耳。先生后孙诸君。属以校雠之役。仍请一言以张之。顾不文何敢当。既请之益勤而辞不获。则敬为之纂次。书
遗说。推以求之于民彝物则之懿。反以验之于躬行心得之蕴。先生之于斯术。可谓积之厚而资之深也。苟使进为时用。少试其所学。岂无有可观。而竟未免穷老江湖。但取紫阳翁沧洲诗语以自号焉。若其晚来一命。虽可见公议之犹不泯于异己者。而其柰瑶琴之已是无心何。然先生岂果于忘世者哉。凡忧愁愉佚。酣嬉幽适。有动乎中者。或寓之呻吟。或托之佔𠌫。大抵皆伤时悯俗之志。忧道勉学之意。而未尝有一毫尤怨之见于其间。故其叙述则闳博纡馀。辞正而理明。能得作者之典则。其比兴则爽朗沈郁。言畅而气婉。不失风人之旨义。即无论二者之能兼。所以裨世教而敦民彝。顾不在是欤。呜乎。此特先生之尘垢耳。糠秕耳。曷足以尽先生。然欲寻其影响。则亦舍是而无以为矣。丹穴一羽。可用为仪。黄耳一脔。可取为珍。其以为残篇短简而少之哉。吾知是集之传诸后无疑也。所可恨者。彼局于偏胜。骛于诡遇者。嵬然代斲于馆阁之上。血指汗颜而不以为耻。使如先生者。缩手袖间。隐约以毕世焉。未知天意果如何耳。先生后孙诸君。属以校雠之役。仍请一言以张之。顾不文何敢当。既请之益勤而辞不获。则敬为之纂次。书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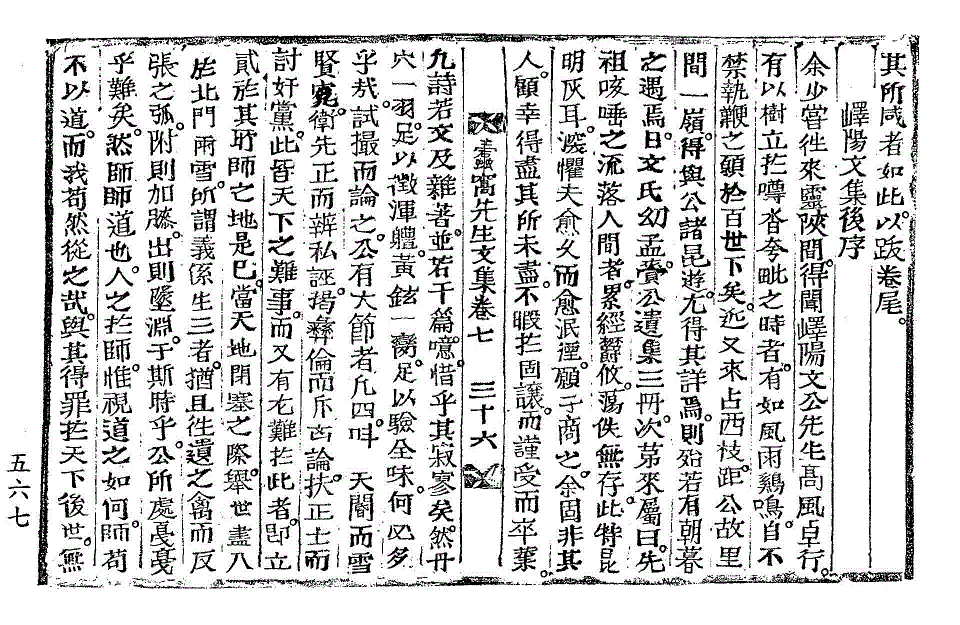 其所咸者如此。以跋卷尾。
其所咸者如此。以跋卷尾。峄阳文集后序
余少尝往来灵陜间。得闻峄阳文公先生高风卓行。有以树立于噂沓夸毗之时者。有如风雨鸡鸣。自不禁执鞭之愿于百世下矣。近又来占西枝。距公故里间一岭。得与公诸昆游。尤得其详焉。则殆若有朝暮之遇焉。日文氏幼孟。赍公遗集三册。次第来属曰。先祖咳唾之流落人间者。累经郁攸。荡佚无存。此特昆明灰耳。深惧夫愈久而愈泯湮。愿子商之。余固非其人。顾幸得尽其所未尽。不暇于固让。而谨受而卒业。凡诗若文及杂著。并若干篇。噫。惜乎其寂寥矣。然丹穴一羽。足以徵浑体。黄铉一脔。足以验全味。何必多乎哉。试撮而论之。公有大节者凡四。叫 天阍而雪贤冤。卫先正而辨私诬。揭彝伦而斥凶论。扶正士而讨奸党。此皆天下之难事。而又有尤难于此者。即立贰于其所师之地是已。当天地闭塞之际。举世尽入于北门雨雪。所谓义系生三者。犹且往遗之禽而反张之弧。附则加膝。出则坠渊。于斯时乎。公所处戛戛乎难矣。然师师道也。人之于师。惟视道之如何。师苟不以道。而我苟然从之哉。与其得罪于天下后世。无
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8H 页
 宁得罪于一时。而甘心坎轲。没齿而无悔焉。今以所处之若是甚难。而所见若是甚高。所守若是甚确。苟非笃于自信而精于见义。有不能及焉。平日学问之力。亦不可诬矣。窃观公所作东行录,君子溪记。其从师讲道之勤。隐居求志之实。备见于其中而有足以知。其早岁之趍向。晚年之造诣也。又观公所尝读朱文心经二书。其于朱文。则逐篇题头。手自圈点。以志其所读遍数。而或至一二百遍。或至三四百遍。时遇有会心处。鼓舞蹈抃之。墨迹笔痕。宛然如隔晨。其所以潜心玩味于敬义博约之训。研精覃思于儒禅王霸之辨。有如夫子所谓浸沈浓郁。优游厌饫者。而至其论伦纪之处变。朋友之急难。则知必有慨然兴起者存。不然何其事之若合符契乎。其于心经。则尽取溪门讲录。凡文义之解释。字句之音读。一一传誊于卷内而无所违意者。月川先生尝为其地主。与之从游还往。而得有以讲问而传受也。惟彼倻山以南。何尝用是录哉。而乃能独尊信。有如字说方盛而暗诵龙门遗韵。优戏方张而私刊云谷笺注。则公可谓溪门之私淑人乎。而异日之立帜贰论。于是乎权舆矣。此盖学问正故心术正。心术正故义理正。义理正故
宁得罪于一时。而甘心坎轲。没齿而无悔焉。今以所处之若是甚难。而所见若是甚高。所守若是甚确。苟非笃于自信而精于见义。有不能及焉。平日学问之力。亦不可诬矣。窃观公所作东行录,君子溪记。其从师讲道之勤。隐居求志之实。备见于其中而有足以知。其早岁之趍向。晚年之造诣也。又观公所尝读朱文心经二书。其于朱文。则逐篇题头。手自圈点。以志其所读遍数。而或至一二百遍。或至三四百遍。时遇有会心处。鼓舞蹈抃之。墨迹笔痕。宛然如隔晨。其所以潜心玩味于敬义博约之训。研精覃思于儒禅王霸之辨。有如夫子所谓浸沈浓郁。优游厌饫者。而至其论伦纪之处变。朋友之急难。则知必有慨然兴起者存。不然何其事之若合符契乎。其于心经。则尽取溪门讲录。凡文义之解释。字句之音读。一一传誊于卷内而无所违意者。月川先生尝为其地主。与之从游还往。而得有以讲问而传受也。惟彼倻山以南。何尝用是录哉。而乃能独尊信。有如字说方盛而暗诵龙门遗韵。优戏方张而私刊云谷笺注。则公可谓溪门之私淑人乎。而异日之立帜贰论。于是乎权舆矣。此盖学问正故心术正。心术正故义理正。义理正故蠹窝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568L 页
 其发于辞气著于行事者。无不一于正。而光明隽洁。魁伟卓荦。是岂得之于飒爽之馀。取次之顷者哉。然逮 朝廷清明。群咻众呴。云消雾歇。而公独不及见。恨不能起九原于当时也。然庚壬两疏。至今为籍口者所龂龂。噫。天下无真是非久矣。惟待千载后公眼而已。又何足多辨。第观后来诸名胜为公发挥者。非不盼然勤矣。而率皆弊弊于粗迹末节。至如学问纯深。义理微密。不少概见。其亦浅之乎知公也。惟有小山李公之序。是为执的论乎。余为之慨然。既次其编第。因书所感者如此。以应文氏之求。而编尾之。系以北人疏劄。窃取义于程朱书末。必录孔沈疏之已例云尔。
其发于辞气著于行事者。无不一于正。而光明隽洁。魁伟卓荦。是岂得之于飒爽之馀。取次之顷者哉。然逮 朝廷清明。群咻众呴。云消雾歇。而公独不及见。恨不能起九原于当时也。然庚壬两疏。至今为籍口者所龂龂。噫。天下无真是非久矣。惟待千载后公眼而已。又何足多辨。第观后来诸名胜为公发挥者。非不盼然勤矣。而率皆弊弊于粗迹末节。至如学问纯深。义理微密。不少概见。其亦浅之乎知公也。惟有小山李公之序。是为执的论乎。余为之慨然。既次其编第。因书所感者如此。以应文氏之求。而编尾之。系以北人疏劄。窃取义于程朱书末。必录孔沈疏之已例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