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x 页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杂著
杂著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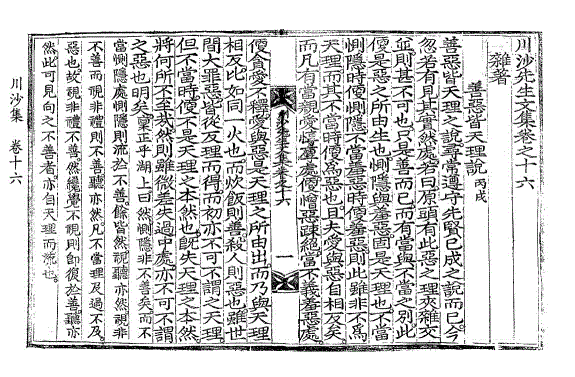 善恶皆天理说(丙戌)
善恶皆天理说(丙戌)善恶皆天理之说。寻常遵守先贤已成之说而已。今忽若有见其实然处。若曰。原头有此恶之理夹杂交并。则甚不可也。只是善而已。而有当与不当之别。此便是恶之所由生也。恻隐与羞恶。固是天理也。不当恻隐时便恻隐。不当羞恶时便羞恶。则此虽非不为天理。而其不当时便为恶也。且夫爱与恶自相反矣。而凡有当亲爱惇厚处。便憎恶疏绝。当不义羞恶处。便贪爱不释。爱与恶是天理之所由出。而乃与天理相反。比如同一火也。而炊饭则善。杀人则恶也。虽世间大罪恶。皆从反理而得。而初亦不可不谓之天理。但不当时。便不是天理之本然也。既失天理之本然。将何所不至哉。然则虽微差失过中处。亦不可不谓之恶也明矣。(禀正乎湖上。曰然。恻隐非不善矣。而不当恻隐处恻隐则流于不善。馀皆然。视听亦然。视非不善而视非礼则不善。听亦然。凡不当理及过不及。恶也。故视非礼不善。然才觉不视则即复于善。听亦然。此可见向之不善者。亦自天理而流也。)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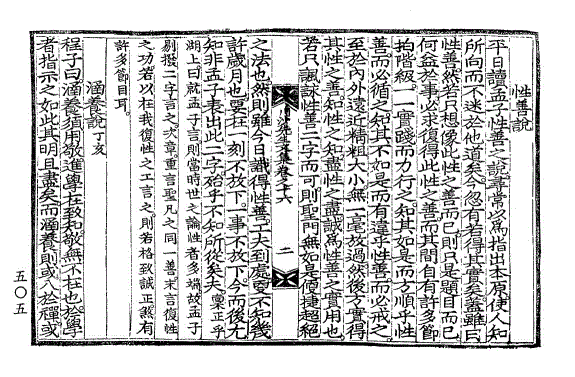 性善说
性善说平日读孟子性善之说。寻常以为指出本原。使人知所向而不迷于他道矣。今忽有若得其实矣。盖虽曰性善。然若只想像此性之善而已。则只是题目而已。何益于事。必求复得此性之善。而其间自有许多节拍阶级。一一实践而力行之。知其如是而方顺乎性善。而必循之。知其不如是而有违乎性善。而必戒之。至于内外远近精粗大小。无一毫放过。然后方实得其性之善。知性之知。尽性之尽。诚为性善之实用也。若只讽咏性善二字而可。则圣门无如是便捷超绝之法也。然则虽今日识得性善。工夫到处。更不知几许岁月也。要在一刻不放下。一事不放下。今而后尤知非孟子表出此二字。殆乎不知所从矣夫。(禀正乎湖上。曰就孟子言。则当时世之论性者多端。故孟子剔拨二字言之。次章。重言圣凡之同一善。末言复性之功。若以在我复性之工言之。则若格致诚正。煞有许多节目耳。)
涵养说(丁亥)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敬无不在也。于学者指示之如此其明且尽矣。而涵养则或入于禅。或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6H 页
 纷纶无主。或昏昧放倒。致知则或索隐穷怪。或穿凿支离。知行无合一之实。动静无相资之妙。近者因自家气质之难胜。日用应接之过当。而体验于践履之违顺。所得之艰裕。则知以上数者之有以致之也。盖其涵养与致知。只是兀然默坐。欲以想像料度存在于冥漠之中而察识于恍惚之馀。虽使有所窥测执定。终是非天理之正。而无用之物事也。是以。养心致知。想见题目。已不胜艰难。未易犯手。寻常言学以二者为要。而实未尝经历谙练沉淹自得于其中矣。日月之间。略见古人之指示。大煞明白。所谓涵养者。未发之时。固宜竖立主宰。有以照管总摄。所谓致知者。天地之物。非不欲物物尽穷。而正好日用明白视听容貌辞气。承上接下。亲疏吉凶之间。精密加工。常有卓立之主宰。而无动静之或失。常辨事物之所具。而验此身之所履。积久而无假借拘束之累。则在我之知。皆是身亲经历者。而明白端的。在心之理。自然存在。而无不得其养矣。此知行所以流通贯洽。而敬直存养之工。该动静而一内外。与夫舍此显然可据之地。而艰辛料度于无形无影者自别。然则静固资益于动。而动亦不为无助于静也。平日所尝诵读之言。
纷纶无主。或昏昧放倒。致知则或索隐穷怪。或穿凿支离。知行无合一之实。动静无相资之妙。近者因自家气质之难胜。日用应接之过当。而体验于践履之违顺。所得之艰裕。则知以上数者之有以致之也。盖其涵养与致知。只是兀然默坐。欲以想像料度存在于冥漠之中而察识于恍惚之馀。虽使有所窥测执定。终是非天理之正。而无用之物事也。是以。养心致知。想见题目。已不胜艰难。未易犯手。寻常言学以二者为要。而实未尝经历谙练沉淹自得于其中矣。日月之间。略见古人之指示。大煞明白。所谓涵养者。未发之时。固宜竖立主宰。有以照管总摄。所谓致知者。天地之物。非不欲物物尽穷。而正好日用明白视听容貌辞气。承上接下。亲疏吉凶之间。精密加工。常有卓立之主宰。而无动静之或失。常辨事物之所具。而验此身之所履。积久而无假借拘束之累。则在我之知。皆是身亲经历者。而明白端的。在心之理。自然存在。而无不得其养矣。此知行所以流通贯洽。而敬直存养之工。该动静而一内外。与夫舍此显然可据之地。而艰辛料度于无形无影者自别。然则静固资益于动。而动亦不为无助于静也。平日所尝诵读之言。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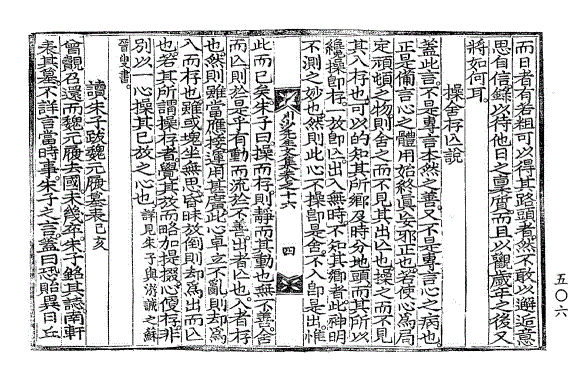 而日者有若粗可以得其路头者。然不敢以邂逅意思自信。录以待他日之禀质。而且以观岁年之后又将如何耳。
而日者有若粗可以得其路头者。然不敢以邂逅意思自信。录以待他日之禀质。而且以观岁年之后又将如何耳。操舍存亡说
盖此言。不是专言本然之善。又不是专言心之病也。正是备言心之体用始终真妄邪正也。若使心为局定顽顿之物。则舍之而不见其出亡也。操之而不见其入存也。可以的知其所乡及时分地头。而其所以才操即存。一放即亡。出入无时。不知其乡者。此神明不测之妙也。然则此心不操即是舍。不入即是出。惟此而已矣。朱子曰。操而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舍而亡。则于是乎有动而流于不善。出者亡也。入者存也。然则虽当应接。运用甚广。此心卓立不乱则却为入而存也。虽或块坐无思。昏昧放倒则却为出而亡也。若其所谓操存者。觉其放而略加提掇。心便存。非别以一心操其已放之心也。(详见朱子与游诚之苏晋叟书。)
读朱子跋魏元履墓表(己亥)
曾觌召还而魏元履去国。未几卒。朱子铭其志。南轩表其墓。不详言当时事。朱子之言。盖曰恐贻异日丘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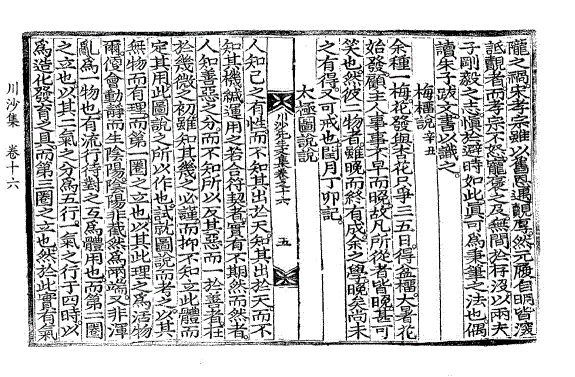 陇之祸。宋孝宗虽以旧恩遇觌厚。然元履自明皆深诋觌者。而孝宗不怒。宠褒之及。无间于存没。以两夫子刚毅之志。慎于避时如此。真可为秉笔之法也。偶读朱子跋文。书以识之。
陇之祸。宋孝宗虽以旧恩遇觌厚。然元履自明皆深诋觌者。而孝宗不怒。宠褒之及。无间于存没。以两夫子刚毅之志。慎于避时如此。真可为秉笔之法也。偶读朱子跋文。书以识之。梅榴说(辛丑)
余种一梅。花发与杏花只争三五日。得盆榴。大暑花始发。顾主人事事不早而晚。故凡所从者皆晚。甚可笑也。然彼二物者。虽晚而终有成。余之学。晚矣尚未之有得。又可戒也。闰月丁卯记。
太极图说说
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其出于天。而不知其机缄运用之若合符契者。实有不期然而然者。人知善恶之分。而不知所以反其恶而一于善者。在于几微之初。虽知其几之必谨。而抑不知立此体而定其用。此图说之所以作也。试就图说而考之。以其无物而有理。而第一圈之立也。以其此理之为活物尔。便会动静而生阴阳。阴阳非截然为两端。又非浑乱为一物也。有流行待对之互为体用也。而第二圈之立也。以其二气之分为五行。一气之行于四时。以为造化发育之具。而第三圈之立也。然于此实有气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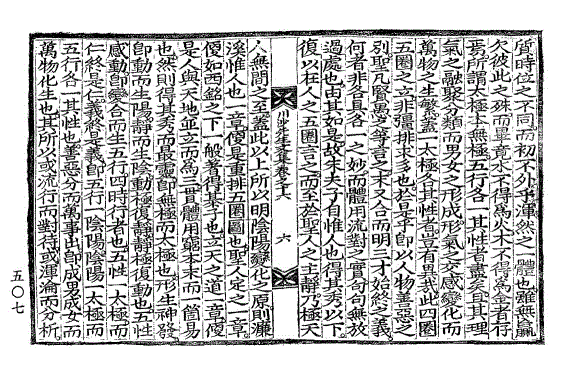 质时位之不同。而初不外乎浑然之一体也。虽无赢欠彼此之殊。而毕竟水不得为火。木不得为金者存焉。所谓太极本无极。五行各一其性者尽矣。且其理气之融聚分类而男女之形成。形气之交感变化而万物之生繁。盖一太极各其性者。岂有异哉。此四圈五圈之立。非彊排求多也。于是乎即以人物善恶之别。圣凡贤愚之等言之。末又合而明三才始终之义。何者非各具各一之妙。而体用流对之实。句句无放过处也。由其如是。故朱夫子自惟人也得其秀以下。复以在人之五圈言之。而至于圣人之主静。乃极天人无间之至。盖此以上所以明阴阳变化之原。则濂溪惟人也一章。便是重排五圈图也。圣人定之一章。便如西铭之下一般著得棋子也。立天之道一章。便是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贯体用穷本末而一个易也。然则得其秀而最灵。即无极而太极也。形生神发。即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也。五性感动。即变合而生五行。四时行者也。五性一太极。而仁终是仁。义终是义。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而五行各一其性也。善恶分而万事出。即成男成女而万物化生也。其所以或流行而对待。或浑沦而分析。
质时位之不同。而初不外乎浑然之一体也。虽无赢欠彼此之殊。而毕竟水不得为火。木不得为金者存焉。所谓太极本无极。五行各一其性者尽矣。且其理气之融聚分类而男女之形成。形气之交感变化而万物之生繁。盖一太极各其性者。岂有异哉。此四圈五圈之立。非彊排求多也。于是乎即以人物善恶之别。圣凡贤愚之等言之。末又合而明三才始终之义。何者非各具各一之妙。而体用流对之实。句句无放过处也。由其如是。故朱夫子自惟人也得其秀以下。复以在人之五圈言之。而至于圣人之主静。乃极天人无间之至。盖此以上所以明阴阳变化之原。则濂溪惟人也一章。便是重排五圈图也。圣人定之一章。便如西铭之下一般著得棋子也。立天之道一章。便是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贯体用穷本末而一个易也。然则得其秀而最灵。即无极而太极也。形生神发。即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也。五性感动。即变合而生五行。四时行者也。五性一太极。而仁终是仁。义终是义。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而五行各一其性也。善恶分而万事出。即成男成女而万物化生也。其所以或流行而对待。或浑沦而分析。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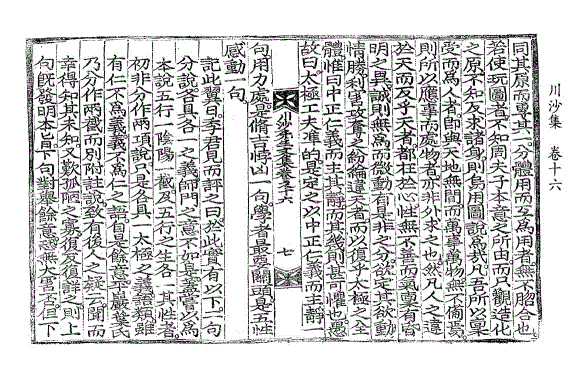 同其原而专其一。分体用而互为用者。无不吻合也。若使玩图者。不知周夫子本意之所由。而只观造化之原。不知反求诸身。则乌用图说为哉。凡吾所以禀受而为人者。即与天地无间。而万事万物。无不备焉。则所以应事而处物者。亦非外求之也。然凡人之违于天而反乎天者。都在于心。性无不善而气禀有昏明之异。诚则无为而微动有是非之分。欲定其欲动情胜。利害攻夺之纷纶违天者。而以复乎太极之全体。惟曰中正仁义而主其静。而其几则甚可惧也。愚故曰。太极工夫准的。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用力处。是脩吉悖凶一句。学者最要关头。是五性感动一句。
同其原而专其一。分体用而互为用者。无不吻合也。若使玩图者。不知周夫子本意之所由。而只观造化之原。不知反求诸身。则乌用图说为哉。凡吾所以禀受而为人者。即与天地无间。而万事万物。无不备焉。则所以应事而处物者。亦非外求之也。然凡人之违于天而反乎天者。都在于心。性无不善而气禀有昏明之异。诚则无为而微动有是非之分。欲定其欲动情胜。利害攻夺之纷纶违天者。而以复乎太极之全体。惟曰中正仁义而主其静。而其几则甚可惧也。愚故曰。太极工夫准的。是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一句。用力处。是脩吉悖凶一句。学者最要关头。是五性感动一句。记此翼日。季君见而评之曰。于此实有以下。二句分说。各具各一之义。师门之意不如是。盖尝以为本说五行一阴阳一截。及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初非分作两项说。只是各具一太极之义。语类。虽有仁不为义。义不为仁之语。自是馀意。平岩叶氏乃分作两截而别附注说。致有后人之疑云。闻而幸得知其未知。又叹孤陋之寡。复反复详之。则上句既发明本旨。下句对举馀意。恐无大害否。但下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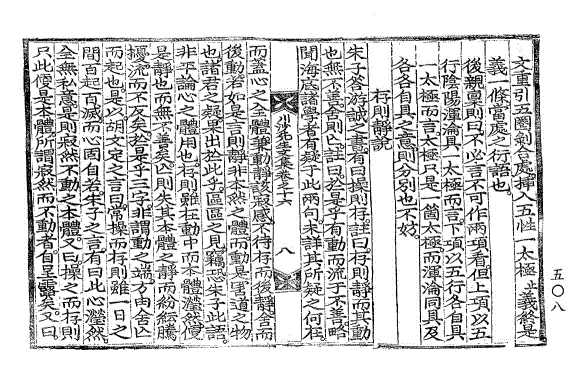 文重引五圈剥合处。插入五性一太极(止)义终是义一条。当处之衍语也。
文重引五圈剥合处。插入五性一太极(止)义终是义一条。当处之衍语也。后亲禀则曰。不必言不可作两项看。但上项以五行阴阳浑沦具一太极而言。下项以五行各自具一太极而言。太极只是一个太极。而浑沦同具及各各自具之意。则分别也不妨。
存则静说
朱子答游诚之书。有曰操则存。注曰。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舍则亡。注曰。于是乎有动而流于不善。略闻海底诸学者有疑于此两句。未详其所疑之何在。而盖心之全体。兼动静该寂感。不待存而后静。舍而后动。若如是言则静非本然之体。而动是害道之物也。诸君之疑。果出于此乎。区区之见。窃恐朱子此语。非平论心之体用也。存则虽在动中而本体滢然。便是静也而无不善矣。亡则失其本体之静而纷纭腾扰。流而不反矣。于是乎三字。非谓动之端。方由舍亡而起也。是以。胡文定之言曰。常操而存则虽一日之间百起百灭。而心固自若。朱子之言。有曰此心滢然。全无私意。是则寂然不动之本体。又曰。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所谓寂然而不动者。自呈露矣。又曰。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9H 页
 感物之际。品节不差。物各止其所则其湛然之体依然。故在亦不害为动中之静也。合此数说而详味之。存则静之义。晓然无可疑。反而观之。亡则动者。自解了矣。要禀此意于诸君。以得一定之论。未敢轻发。私志以俟云。
感物之际。品节不差。物各止其所则其湛然之体依然。故在亦不害为动中之静也。合此数说而详味之。存则静之义。晓然无可疑。反而观之。亡则动者。自解了矣。要禀此意于诸君。以得一定之论。未敢轻发。私志以俟云。书李学甫誊示张敬堂性道说
金子高问。前日则指性为统体一太极。后日则指道为统体一太极。前后之说不同。答曰。前日则据朱子论未发处不滞一隅。不拘一时之说。故指性为统体一太极。后日则主太极生两仪之说。故指道为统体一太极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此道字。兼性情而言者。然则性者道之体立。而情者道之用行之谓。此谓道为统体一太极之说也。又曰道统性情者也。○赠表侄。天命之性者体也。率性之道者用也。体者浑然全体之名。用者灿然条贯之称。此道流行于日用之间。而非人体之则人自人。道自道。在我之理。或几乎息矣。○赠李晦叔。性者道之体也。道者性之用也。此之谓道之全体也。大而天地。小而事物细微。无一不具于此道之中。大化流行。未尝间断。而必待人而后行。必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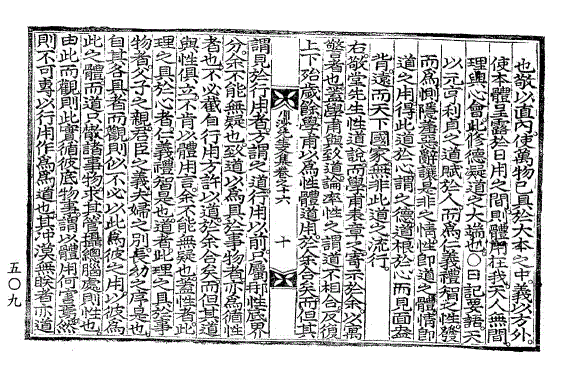 也敬以直内。使万物已具于大本之中。义以方外。使本体呈露于日用之间。则体用在我。天人无间。理与心会。此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日记要语。天以元亨利贞之道赋于人。而为仁义礼智之性。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性即道之体。情即道之用。得此道于心。谓之德。道根于心而见面盎背。远而天下国家。无非此道之流行。
也敬以直内。使万物已具于大本之中。义以方外。使本体呈露于日用之间。则体用在我。天人无间。理与心会。此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日记要语。天以元亨利贞之道赋于人。而为仁义礼智之性。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性即道之体。情即道之用。得此道于心。谓之德。道根于心而见面盎背。远而天下国家。无非此道之流行。右。敬堂先生性道说。而学甫表章之。寄示于余。以寓警者也。盖学甫与致道。论率性之谓道不相合。反复上下殆岁馀。学甫以为性体道用。于余合矣。而但其谓见于行用者。方谓之道。行用以前。只属那性底界分。余不能无疑也。致道以为具于事物者。亦为循性者也。不必截自行用方许以道。于余合矣。而但其道与性俱立。不肯以体用言。余不能无疑也。盖性者。此理之具于心者。仁义礼智是也。道者。此理之具于事物者。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是也。自其各具者而观则似不必以此为彼之用。以彼为此之体。而道只散诸事物。求其管摄总脑处则性也。由此而观则此实循彼底物事。谓以体用何害焉。然则不可专以行用作为为道也。其冲漠无眹者亦道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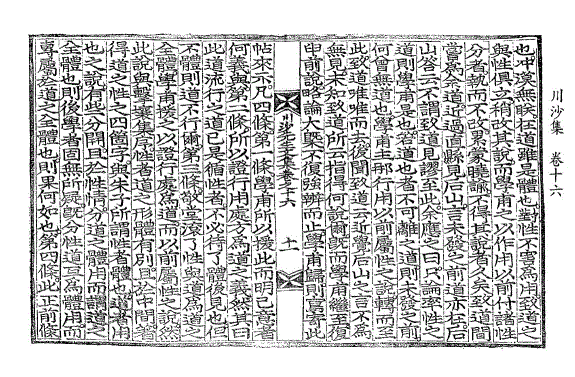 也。冲漠无眹。在道虽是体也。对性不害为用。致道之与性俱立。稍改其说。而学甫之以作用以前付诸性分者。执而不改。累蒙晓谕。不得其说者久矣。致道间尝为余道。近过直县见后山。言未发之前道亦在。后山答云不谓致道见谬至此。余应之曰。只论率性之道则学甫是也。若道也者不可离之道。则未发之前。何曾无道也。学甫主那行用以前属性之说。转而至此。致道唯唯而去。后闻致道云近觉后山之言不为无见。未知致道所云指得何说尔。既而学甫继至。复申前说。略论大槩。不复强辨而止。学甫归。则写寄此帖来示。凡四条。第一条。学甫所以援此而明己意者何义与。第二条。所以證行用处方为道之义。然其曰此道流行之道已是循性者。不必待了体后见也。但不体则道不行尔。第三条。敬堂滚了性与道为道之全体。学甫援之以證行处为道。而以前属性之说。然此说与击壤集序。性者道之形体有别。且于中间。著得道之性之四个字。与朱子所谓性者体也。道者用也之说。有些分开。且于性情。分道之体用而谓道之全体也。则后学者固无所疑。既分性道互为体用。而专属于道之全体也。则果何如也。第四条。此正前条
也。冲漠无眹。在道虽是体也。对性不害为用。致道之与性俱立。稍改其说。而学甫之以作用以前付诸性分者。执而不改。累蒙晓谕。不得其说者久矣。致道间尝为余道。近过直县见后山。言未发之前道亦在。后山答云不谓致道见谬至此。余应之曰。只论率性之道则学甫是也。若道也者不可离之道。则未发之前。何曾无道也。学甫主那行用以前属性之说。转而至此。致道唯唯而去。后闻致道云近觉后山之言不为无见。未知致道所云指得何说尔。既而学甫继至。复申前说。略论大槩。不复强辨而止。学甫归。则写寄此帖来示。凡四条。第一条。学甫所以援此而明己意者何义与。第二条。所以證行用处方为道之义。然其曰此道流行之道已是循性者。不必待了体后见也。但不体则道不行尔。第三条。敬堂滚了性与道为道之全体。学甫援之以證行处为道。而以前属性之说。然此说与击壤集序。性者道之形体有别。且于中间。著得道之性之四个字。与朱子所谓性者体也。道者用也之说。有些分开。且于性情。分道之体用而谓道之全体也。则后学者固无所疑。既分性道互为体用。而专属于道之全体也。则果何如也。第四条。此正前条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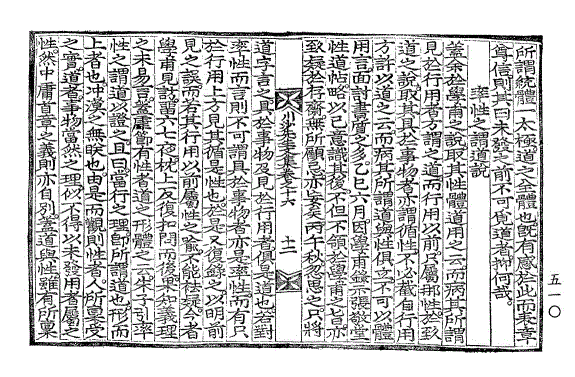 所谓统体一太极。道之全体也。既有感于此而表章尊信。则其曰未发之前不可觅道者。抑何哉。
所谓统体一太极。道之全体也。既有感于此而表章尊信。则其曰未发之前不可觅道者。抑何哉。率性之谓道说
盖余于学甫之说。取其性体道用之云。而病其所谓见于行用者方谓之道。而行用以前。只属那性。于致道之说。取其具于事物者亦谓循性。不必截自行用方许以道之云。而病其所谓道与性俱立。不可以体用言。面讨书质之多。乙巳六月。因学甫录示张敬堂性道帖。略以己意识其后。不但不领于学甫之旨。亦致疑于存斋。无所顾忌。亦妄矣。丙午秋。忽思之。只将道字言之。具于事物及见于行用者。俱是道也。若对率性而言则不可谓具于事物者亦是率性。而有只于行用上方见其循是性也。于是又复录之。以明前见之误。而若其行用以前属性之喻。不能祛疑。今者学甫见访。留六七夜。枕上反复扣问而后。果知义理之未易言。盖康节有性者道之形体之云。朱子引率性之谓道以證之。且曰。当行之理。即所谓道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无眹也。由是而观则性者。人所禀受之实。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似不得以未发用者属之性。然中庸首章之义则亦自别。盖道与性。虽有所禀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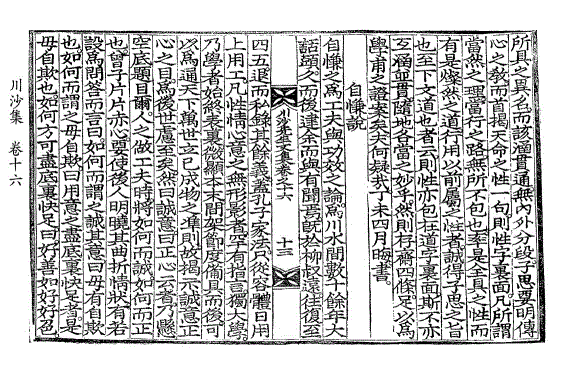 所具之异名。而该涵贯通。无内外分段。子思要明传心之教。而首揭天命之性一句。则性字里面。凡所谓当然之理。当行之路。无所不包也。率是全具之性而有是灿然之道。行用以前属之性者。诚得子思之旨也。至下文道也者云。则性亦包在道字里面。斯不亦互涵并贯。随地各当之妙乎。然则存斋四条。足以为学甫之證案矣。夫何疑哉。丁未四月晦。书。
所具之异名。而该涵贯通。无内外分段。子思要明传心之教。而首揭天命之性一句。则性字里面。凡所谓当然之理。当行之路。无所不包也。率是全具之性而有是灿然之道。行用以前属之性者。诚得子思之旨也。至下文道也者云。则性亦包在道字里面。斯不亦互涵并贯。随地各当之妙乎。然则存斋四条。足以为学甫之證案矣。夫何疑哉。丁未四月晦。书。自慊说
自慊之为工夫与功效之论。为川水间数十馀年大话头。久而后逮余而与有闻焉。既于柳叔远。往复至四五。退而私录其馀义。盖孔子家法。只从容体日用上用工。凡性情心意之无形影者。罕有指言。独大学。乃学者始终表里。微显本末。间架节度备具而后。可以为通天下万世立己成物之准则。故揭示诚意正心之目。为后世虑至矣。然曰诚意。曰正心云者。乃悬空底题目尔。人之做工夫时。将如何而诚。如何而正也。曾子片片赤心。要使后人明晓其曲折情状。有若设为问答而言曰。如何而谓之诚其意。曰毋有自欺也。如何而谓之毋自欺。曰用意之尽底里快足者。是毋自欺也。如何方可尽底里快足。曰。好善如好好色。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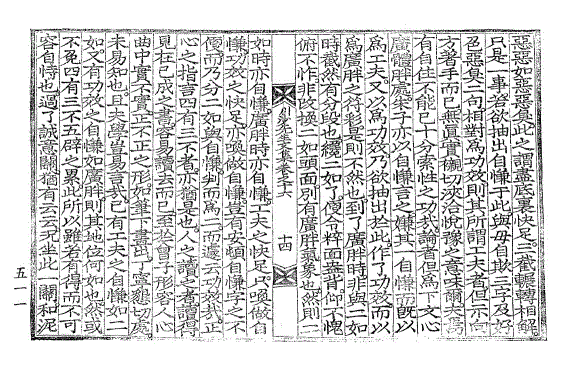 恶恶如恶恶臭。此之谓尽底里快足。三截辗转相解。只是一事。若欲抽出自慊于此。与毋自欺三字及好色恶臭二句。相对为功效。则其所谓工夫者。但示向方著手而已。无真实衬切浃洽悦豫之意味尔。夫焉有自住不能已十分索性之功哉。论者但为下文心广体胖处。朱子亦以自慊言之。嫌其一自慊而既以为工夫。又以为功效。乃欲抽出于此。作了功效。而以为广胖之符彩。是则不然也。到了广胖时。非与二如时截然有分段也。才二如了。便令粹面盎背。仰不愧俯不怍。非改换二如头面。别有广胖气象也。然则二如时亦自慊。广胖时亦自慊。工夫之快足。只唤做自慊。功效之快足。亦唤做自慊。岂有安顿自慊字之不便。而乃分二如与自慊。判而为二。而遽云功效哉。正心之指言四有三不者。亦犹是也。人之读之者。读得见在已成之书。容易读去而已。至于曾子形容人心曲中实不实。正不正之形。如笔下画出。丁宁恳切处。未易知也。且夫学岂易言哉。已有工夫之自慊如二如。又有功效之自慊如广胖。则其地位何如也。然或不免四有三不五辟之累。此所以虽若有得而不可容自恃也。过了诚意关。犹有云云。况坐此一关。和泥
恶恶如恶恶臭。此之谓尽底里快足。三截辗转相解。只是一事。若欲抽出自慊于此。与毋自欺三字及好色恶臭二句。相对为功效。则其所谓工夫者。但示向方著手而已。无真实衬切浃洽悦豫之意味尔。夫焉有自住不能已十分索性之功哉。论者但为下文心广体胖处。朱子亦以自慊言之。嫌其一自慊而既以为工夫。又以为功效。乃欲抽出于此。作了功效。而以为广胖之符彩。是则不然也。到了广胖时。非与二如时截然有分段也。才二如了。便令粹面盎背。仰不愧俯不怍。非改换二如头面。别有广胖气象也。然则二如时亦自慊。广胖时亦自慊。工夫之快足。只唤做自慊。功效之快足。亦唤做自慊。岂有安顿自慊字之不便。而乃分二如与自慊。判而为二。而遽云功效哉。正心之指言四有三不者。亦犹是也。人之读之者。读得见在已成之书。容易读去而已。至于曾子形容人心曲中实不实。正不正之形。如笔下画出。丁宁恳切处。未易知也。且夫学岂易言哉。已有工夫之自慊如二如。又有功效之自慊如广胖。则其地位何如也。然或不免四有三不五辟之累。此所以虽若有得而不可容自恃也。过了诚意关。犹有云云。况坐此一关。和泥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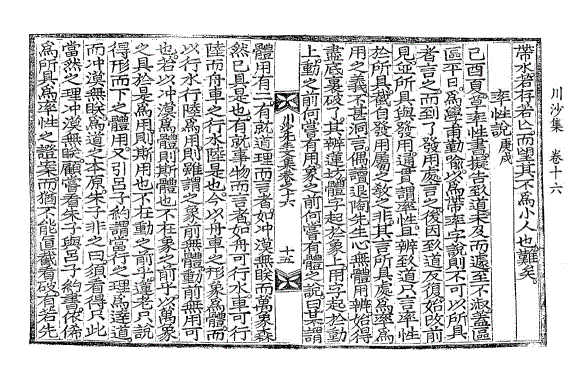 带水。若存若亡。而望其不为小人也。难矣。
带水。若存若亡。而望其不为小人也。难矣。率性说(庚戌)
己酉夏。草率性书。拟告致道。未及而遽至不淑。盖区区平日。为学甫勤喻。以为带率字说则不可以所具者言之。而到了发用处言之。后因致道反复。始改前见。并所具与发用。通贯谓率性。且辨致道只言率性于所具。截自发用属之教之非。其言所具处为率为用之义。不甚洞言。偶读退陶先生心无体用辨。始得尽底里破了。其辨莲坊。体字起于象上。用字起于动上。动之前何尝有用。象之前何尝有体之说。曰某谓体用有二。有就道理而言者。如冲漠无眹而万象森然已具是也。有就事物而言者。如舟可行水。车可行陆而舟车之行水陆是也。今以舟车之形象为体。而以行水行陆为用。则虽谓之象前无体。动前无用可也。若以冲漠为体。则斯体也不在象之前乎。以万象之具于是为用。则斯用也不在动之前乎。莲老只说得形而下之体用。又引吕子约谓当行之理为达道。而冲漠无眹。为道之本原。朱子非之曰。须看得只此当然之理冲漠无眹。顾尝看朱子与吕子约书。依俙为所具为率性之證案。而犹不能直截看破。有若先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2L 页
 知有今日之疑者然如此。信乎契合古训之难也。合两先生说而玩之。所具者亦为用处。指诸掌乎。
知有今日之疑者然如此。信乎契合古训之难也。合两先生说而玩之。所具者亦为用处。指诸掌乎。大山先生碣文中四七说往复修改辨
先师碣文。蔡相公所撰。而有曰先生以为理与气不相杂处。自有不相离者。不可分中。亦有不可不分者。分看合看。莫非全体。在四在七。浑是一物。圣贤之言。有浑沦言时。亦有分开说处。浑沦处作浑沦看。分开处作分开看。于是作四七说。理气汇编。上下语句。皆依先生之说。而其中分看合看。莫非全体。在四在七。浑是一物两句。微有化现做成。上句固无病。而下句差违本旨。盖分看而其四七非在合看之外也。合看而曰四曰七之与分看者初无二义也。则此固无害。不言合看而但曰在四在七为一物。则仁义礼智之端。喜怒哀乐之情。两目对立。名义自别。不可谓一物。而非先生之旨也。玆与同人商量。嘱柳天瑞禀请而改之。
朴南野甲乙录辨(爱之之理。便是仁一条。)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其发则慈爱而恻怛。生生而不穷也。此为元本主材。何有于包涵与贯通哉。然其德也。其理也。煞有体段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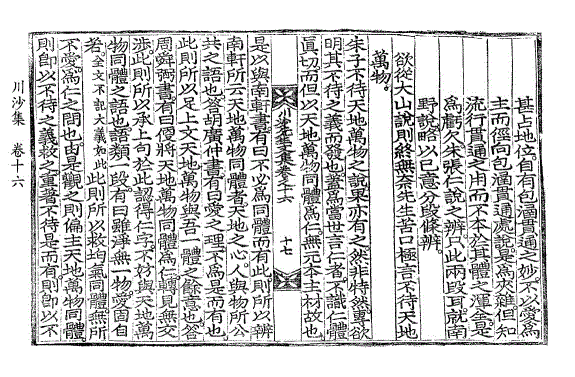 甚占地位。自有包涵贯通之妙。不以爱为主而径向包涵贯通处说。是为夹杂。但知流行贯通之用而不本于其体之浑全。是为亏欠。朱张仁说之辨。只此两段耳。就南野说。略以己意分段条辨。
甚占地位。自有包涵贯通之妙。不以爱为主而径向包涵贯通处说。是为夹杂。但知流行贯通之用而不本于其体之浑全。是为亏欠。朱张仁说之辨。只此两段耳。就南野说。略以己意分段条辨。欲从大山说则终无奈先生苦口极言。不待天地万物。
朱子不待天地万物之说。果亦有之。然非特然。专欲明其不待之义而发也。盖为当世言仁者。不识仁体真切。而但以天地万物同体为仁。无元本主材故也。是以与南轩书。有曰不必为同体而有此。则所以辨南轩所云天地万物同体者。天地之心。人与物所公共之语也。答胡广仲书。有曰爱之理。不为是而有也。此则所以足上文天地万物与吾一体之馀意也。答周舜弼书。有曰便将天地万物同体为仁。转见无交涉。此则所以承上句于此认得仁字。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之语也。语类一段。有曰虽净无一物。爱固自若。(全文不记大义如此)此则所以救均气同体。无所不爱。为仁之问也。由是观之则偏主天地万物同体。则即以不待之义救之。重著不待是而有。则即以不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3L 页
 妨与同体之义申之。双举并立。未或偏重。认其为发明不待之中。自有指示同体之妙。然自汉以来。学者专以爱言仁。而不知其体之如何。二程以后。稍知仁之不止于爱。展转泛滥。不知元本。盖不明不待之义则仁为空荡之料。不明同体之妙则仁为私己之物。朱子忧患之意备矣。然随时救弊之道。发明不待处较切。而只是此数段。非谓主此爱字。则天地万物。于吾不关。闭户绝物。把玩此肚里宝物也。今不言所由。而只曰苦口极言云云。有若朱子只守个一边而看他天地万物为别事。未知如何。
妨与同体之义申之。双举并立。未或偏重。认其为发明不待之中。自有指示同体之妙。然自汉以来。学者专以爱言仁。而不知其体之如何。二程以后。稍知仁之不止于爱。展转泛滥。不知元本。盖不明不待之义则仁为空荡之料。不明同体之妙则仁为私己之物。朱子忧患之意备矣。然随时救弊之道。发明不待处较切。而只是此数段。非谓主此爱字。则天地万物。于吾不关。闭户绝物。把玩此肚里宝物也。今不言所由。而只曰苦口极言云云。有若朱子只守个一边而看他天地万物为别事。未知如何。一矛一盾。至于如此之甚。
既言不待天地万物。而有又言若无则亏欠。又言此理甚约。三句牴牾。便相矛盾之疑无怪。此处仁说之肯綮要旨决矣。盖爱之理一句中。便见元本主材。而即此主材。便有浑涵底体段。非有二也。盖无是主材。无以为流行之本。非是体段。无以为贯通之妙。主本材而言则不关于天地万物之有无。主体段而言则若无天地万物。与甚底为一体而爱何所施乎。故于主材处。说著天地万物为夹杂。于体段上。去了天地万物为亏欠。然则不待万物而有之云。与夫若无则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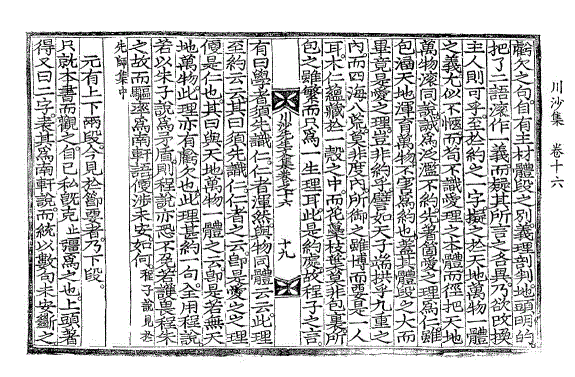 亏欠之句。自有主材体段之别。义理剖判。地头明的。把了二语滚作一义。而疑其所言之各异。乃欲改换主人则可乎。至于约之一字。拟之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义。尤似不惬。而苟不识爱理之本体。而径把天地万物滚同说。诚为泛滥不约。先著个爱之理为仁。虽包涵天地浑育万物。不害为约也。盖其体段之大而毕竟是爱之理。岂非约乎。譬如天子端拱乎九重之内。而四海八荒。莫非度内。所御之虽博而要是一人耳。木仁蕴藏于一壳之中。而花蕊枝叶莫非包里。所包之虽繁而只为一生理耳。此是约处。故程子之言。有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云云。此理至约云云。其曰须先识仁。仁者之云。即是爱之之理便是仁也。其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云。即是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也。此理甚约一句。全用程说。若以朱子说为矛盾。则程说亦恐不免。若护畏程朱之故而驱率为南轩语。便涉未安。如何。(程子说见于先师集中)
亏欠之句。自有主材体段之别。义理剖判。地头明的。把了二语滚作一义。而疑其所言之各异。乃欲改换主人则可乎。至于约之一字。拟之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义。尤似不惬。而苟不识爱理之本体。而径把天地万物滚同说。诚为泛滥不约。先著个爱之理为仁。虽包涵天地浑育万物。不害为约也。盖其体段之大而毕竟是爱之理。岂非约乎。譬如天子端拱乎九重之内。而四海八荒。莫非度内。所御之虽博而要是一人耳。木仁蕴藏于一壳之中。而花蕊枝叶莫非包里。所包之虽繁而只为一生理耳。此是约处。故程子之言。有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云云。此理至约云云。其曰须先识仁。仁者之云。即是爱之之理便是仁也。其曰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云。即是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也。此理甚约一句。全用程说。若以朱子说为矛盾。则程说亦恐不免。若护畏程朱之故而驱率为南轩语。便涉未安。如何。(程子说见于先师集中)元有上下两段。今见于节要者。乃下段。
只就本书而观之。自己私既克(止)彊为之也。上头著得又曰二字。表其为南轩说。而统以数句未安断之。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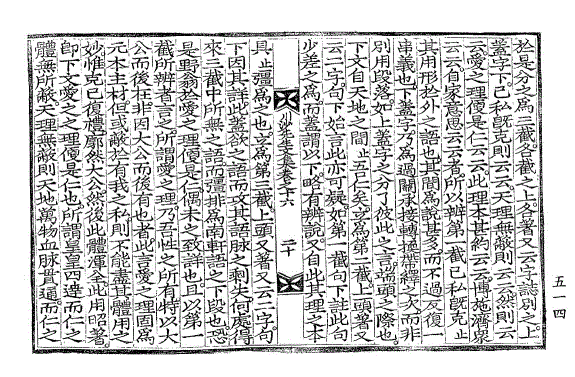 于是分之为三截。各截之上。各著又云字志别之。上盖字下。己私既克则云云。天理无蔽则云云。然则云云。爱之理便是仁云云。此理本甚约云云。博施济众云云。自家意思云云者。所以辨第一截己私既克(止)其用形于外之语也。其间为说甚多。而不过反复一串义也。下盖字。乃为过关承接转换带绎之次。而非别用段落。如上盖字之分了彼此之言。端头之际也。下文自天地之间(止)吾仁矣。立为第二截。上头著又云二字。句下始言此亦可疑。如第一截句下注此句少差之为。而盖谓以下。略有辨说。又自此其理之本具(止)彊为之也。立为第三截。上头又著又云二字。句下因其详。此盖欲之语而攻其语脉之剩失。何处得来三截中所无之语。而彊排为南轩语之下段也。恐是野翁于爱之理便是仁。偶未之致详也。且以第一截所辨者言之。所谓爱之理。乃吾性之所有。特以大公而后在。非因大公而后有也者。此言爱之理固为元本主材。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则不能尽其体用之妙。惟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即下文爱之之理便是仁也。所谓皇皇四达而仁之体无所蔽。天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仁之
于是分之为三截。各截之上。各著又云字志别之。上盖字下。己私既克则云云。天理无蔽则云云。然则云云。爱之理便是仁云云。此理本甚约云云。博施济众云云。自家意思云云者。所以辨第一截己私既克(止)其用形于外之语也。其间为说甚多。而不过反复一串义也。下盖字。乃为过关承接转换带绎之次。而非别用段落。如上盖字之分了彼此之言。端头之际也。下文自天地之间(止)吾仁矣。立为第二截。上头著又云二字。句下始言此亦可疑。如第一截句下注此句少差之为。而盖谓以下。略有辨说。又自此其理之本具(止)彊为之也。立为第三截。上头又著又云二字。句下因其详。此盖欲之语而攻其语脉之剩失。何处得来三截中所无之语。而彊排为南轩语之下段也。恐是野翁于爱之理便是仁。偶未之致详也。且以第一截所辨者言之。所谓爱之理。乃吾性之所有。特以大公而后在。非因大公而后有也者。此言爱之理固为元本主材。但或蔽于有我之私。则不能尽其体用之妙。惟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即下文爱之之理便是仁也。所谓皇皇四达而仁之体无所蔽。天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仁之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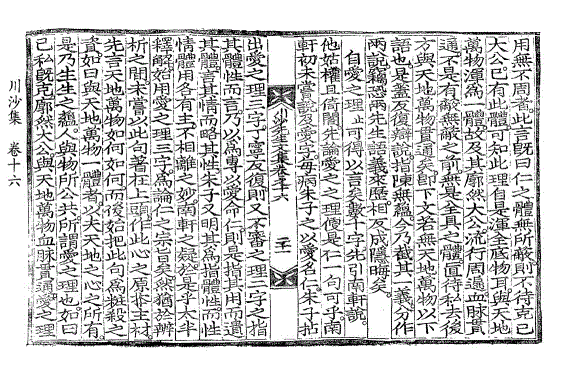 用无不周者。此言既曰仁之体无所蔽。则不待克己大公。已有此体。可知此理自是浑全底物耳。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故及其廓然大公。流行周遍。血脉贯通。不是有蔽无蔽之前。无是全具之体。直待私去后方与天地万物贯通矣。即下文若无天地万物以下语也。是盖反复辩说。指陈无蕴。今乃截其一义。分作两说。窃恐两先生语义来历。相反成隐晦矣。
用无不周者。此言既曰仁之体无所蔽。则不待克己大公。已有此体。可知此理自是浑全底物耳。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故及其廓然大公。流行周遍。血脉贯通。不是有蔽无蔽之前。无是全具之体。直待私去后方与天地万物贯通矣。即下文若无天地万物以下语也。是盖反复辩说。指陈无蕴。今乃截其一义。分作两说。窃恐两先生语义来历。相反成隐晦矣。自爱之理(止)可得以言矣数十字。先引南轩说。
他姑权且倚阁。先论爱之之理便是仁一句可乎。南轩初未尝说及爱字。每病朱子之以爱名仁。朱子拈出爱之理三字。丁宁反复。则又不审之理二字之指其体性而言。乃以为专以爱命仁。则是指其用而遗其体。言其情而略其性。朱子又明其为指体性。而性情体用各有主。不相离之妙。南轩之疑。于是乎太半释解。始用爱之理三字。为论仁之宗旨矣。然犹于辨析之间。未尝以此句著在上头。作此心之原本主材。先言天地万物如何如何。而后始把此句为妆杀之资。如曰与天地万物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蕴。人与物所公共。所谓爱之理也。如曰己私既克。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爱之理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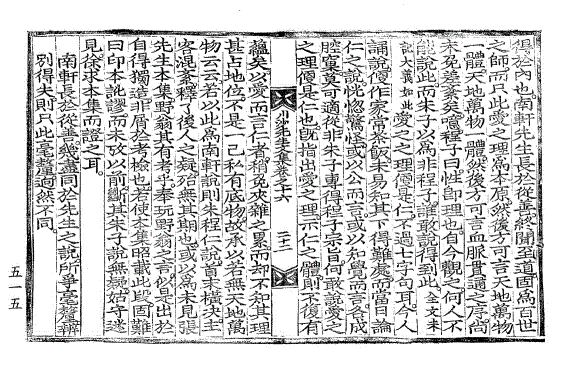 得于内也。南轩先生长于从善。终闻至道。固为百世之师。而只此爱之理为本原。然后方可言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一体。然后方可言血脉贯通之序。尚未免差紊矣。噫。程子曰。性即理也。自今观之。何人不能说此。而朱子以为非程子。谁敢说得到此。(全文未记大义如此)爱之之理便是仁。不过七字句耳。今人诵说。便作家常茶饭。未易知其下得难处。而当日论仁之说。恍惚惊怪。或以公而言。或以知觉而言。各成腔窠。莫可适从。非朱子专得程子宗旨。何敢说爱之之理便是仁也。既指出爱之理。示仁之体。则不复有蕴矣。以爱而言仁者。稍免夹杂之累。而却不知其理甚占地位。不是一己私有底物。故承以若无天地万物云云。若以此为南轩说则朱程仁说。首末横决。主客混紊。释了后人之疑。殆无其期也。或以为未见张先生本集。野翁其有考乎。奉玩野翁之言。似是出于自得独造。非屑于考检也。若使本集昭载此段。固难曰印本讹谬。而未考以前。断其朱子说无疑。姑守迷见。徐求本集而證之耳。
得于内也。南轩先生长于从善。终闻至道。固为百世之师。而只此爱之理为本原。然后方可言天地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一体。然后方可言血脉贯通之序。尚未免差紊矣。噫。程子曰。性即理也。自今观之。何人不能说此。而朱子以为非程子。谁敢说得到此。(全文未记大义如此)爱之之理便是仁。不过七字句耳。今人诵说。便作家常茶饭。未易知其下得难处。而当日论仁之说。恍惚惊怪。或以公而言。或以知觉而言。各成腔窠。莫可适从。非朱子专得程子宗旨。何敢说爱之之理便是仁也。既指出爱之理。示仁之体。则不复有蕴矣。以爱而言仁者。稍免夹杂之累。而却不知其理甚占地位。不是一己私有底物。故承以若无天地万物云云。若以此为南轩说则朱程仁说。首末横决。主客混紊。释了后人之疑。殆无其期也。或以为未见张先生本集。野翁其有考乎。奉玩野翁之言。似是出于自得独造。非屑于考检也。若使本集昭载此段。固难曰印本讹谬。而未考以前。断其朱子说无疑。姑守迷见。徐求本集而證之耳。南轩长于从善。几尽同于先生之说。所争毫釐。辨别得失。则只此毫釐。迥然不同。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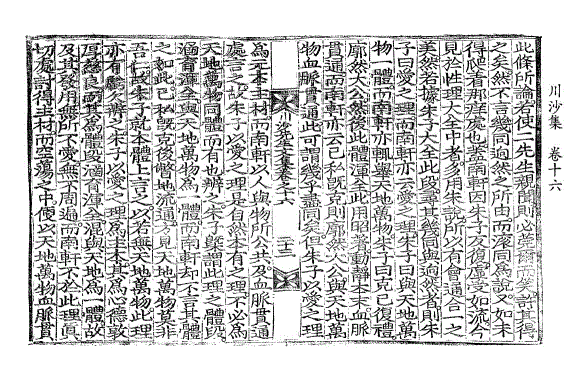 此条所论。若使二先生亲闻。则必莞尔而笑。许其得之矣。然不言几同迥然之所由。而滚同为说。又如未得爬着那痒处也。盖南轩因朱子反复。虚受如流。今见于性理大全中者。多用朱说。所以有会通合一之美。然若据朱子大全此段。寻其几同与迥然者。则朱子曰爱之理。而南轩亦云爱之理。朱子曰与天地万物一体。而南轩亦辄举天地万物。朱子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而南轩亦云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此可谓几乎尽同矣。但朱子以爱之理为元本主材。而南轩以人与物所公共。及血脉贯通处言之。故朱子以爱之理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有也辨之。朱子槩谓此理之体段。涵育浑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南轩却不言其体之如此。己私既克后瞥地流通。方见天地万物莫非吾仁。故朱子就本体上言之。以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辨之。朱子以爱之理为主本。其为心德敦厚慈良。而其为体段涵育浑全。混与天地为一体。故及其发用。无所不爱。无不周遍。而南轩不于此理真切处讨得主材。而空荡之中。便以天地万物血脉贯
此条所论。若使二先生亲闻。则必莞尔而笑。许其得之矣。然不言几同迥然之所由。而滚同为说。又如未得爬着那痒处也。盖南轩因朱子反复。虚受如流。今见于性理大全中者。多用朱说。所以有会通合一之美。然若据朱子大全此段。寻其几同与迥然者。则朱子曰爱之理。而南轩亦云爱之理。朱子曰与天地万物一体。而南轩亦辄举天地万物。朱子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而南轩亦云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此可谓几乎尽同矣。但朱子以爱之理为元本主材。而南轩以人与物所公共。及血脉贯通处言之。故朱子以爱之理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有也辨之。朱子槩谓此理之体段。涵育浑全。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南轩却不言其体之如此。己私既克后瞥地流通。方见天地万物莫非吾仁。故朱子就本体上言之。以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辨之。朱子以爱之理为主本。其为心德敦厚慈良。而其为体段涵育浑全。混与天地为一体。故及其发用。无所不爱。无不周遍。而南轩不于此理真切处讨得主材。而空荡之中。便以天地万物血脉贯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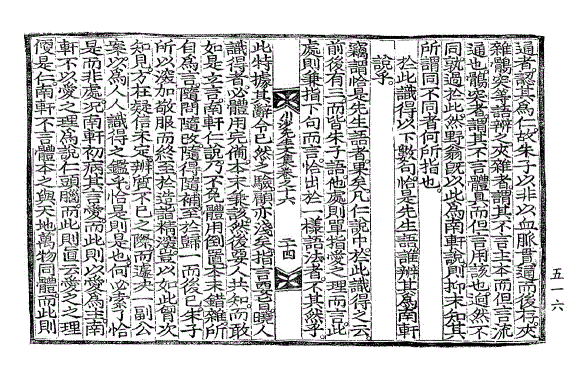 通者。认其为仁。故朱子以非以血脉贯通而后存。夹杂鹘突等语辨之。夹杂者。谓其不言主本而但言流通也。鹘突者。谓其不言体具而但言用该也。迥然不同。孰过于此。然野翁既以此为南轩说。则抑未知其所谓同不同者何所指也。
通者。认其为仁。故朱子以非以血脉贯通而后存。夹杂鹘突等语辨之。夹杂者。谓其不言主本而但言流通也。鹘突者。谓其不言体具而但言用该也。迥然不同。孰过于此。然野翁既以此为南轩说。则抑未知其所谓同不同者何所指也。于此识得以下数句。恰是先生语。谁辨其为南轩说乎。
窃谓恰是先生语者。果矣。凡仁说中。于此识得之云。前后有三。而皆朱子语。他处则单指爱之理而言。此处则兼指下句而言。恰出于一样语法者。不其然乎。此特据其辞令已然之验。顾亦浅矣。指言要旨。晓人识得者。必体用完备。本末兼该。然后要人共知。而敢如是立言。南轩仁说。乃不免体用倒置。本末错杂。所自为言。随问随改。随得随补。至于归一而后已。朱子所以深加敬服而终至于造诣精深。岂以如此胸次知见。方在疑信未定。辨质不已之际。而遽决一副公案。以为人人识得之鉴乎。恰是则是也。何必索了恰是而非处。况南轩初病其言爱。而此则以爱为主。南轩不以爱之理为说仁头脑。而此则直云爱之之理便是仁。南轩不言体本之与天地万物同体。而此则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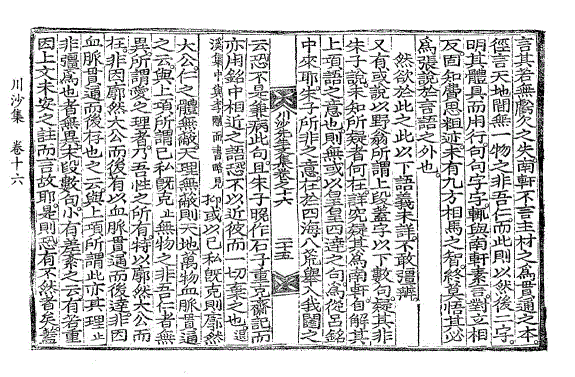 言其若无亏欠之失。南轩不言主材之为贯通之本。径言天地间无一物之非吾仁。而此则以然后二字。明其体具而用行。句句字字。辄与南轩素言。对立相反。固知费思粗迹。未有九方相马之智。终莫悟其必为张说于言语之外也。
言其若无亏欠之失。南轩不言主材之为贯通之本。径言天地间无一物之非吾仁。而此则以然后二字。明其体具而用行。句句字字。辄与南轩素言。对立相反。固知费思粗迹。未有九方相马之智。终莫悟其必为张说于言语之外也。然欲于此之此以下语义未详。不敢彊辨。
又有或说以野翁所谓上段盖字以下数句。疑其非朱子说。未知所疑者何在。详究疑其为南轩。自解其上项语之意也。则无或以皇皇四达之句。为从吕铭中来耶。朱子所非之意。在于四海八荒举入我闼之云。恐不是兼病此句。且朱子晚作石子重克斋记。而亦用铭中相近之语。恐不以近彼而一切弃之也。(退溪集中与李刚而书略见)抑或以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仁之体无蔽。天理无蔽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之云。与上项所谓己私既克(止)无物之非吾仁者无异。所谓爱之理者。乃吾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后有以血脉贯通而后达。非因血脉贯通而后存也之云。与上项所谓此亦其理(止)非彊为也者无异。末段数句。小有差紊之云。有若重因上文未安之注而言故耶。是则恐有不然者矣。盖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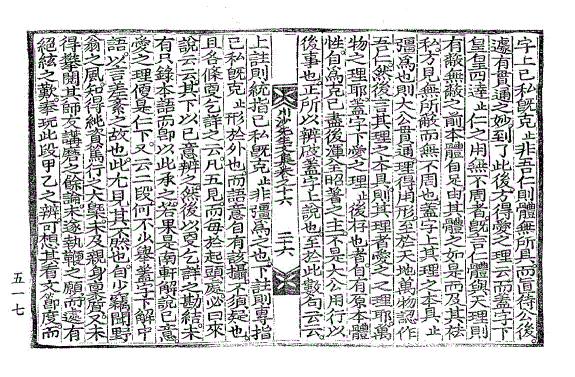 字上己私既克(止)非吾仁则体无所具。而直待公后。遽有贯通之妙。到了此后。方得爱之理云。而盖字下皇皇四达(止)仁之用无不周者。既言仁体与天理则有蔽无蔽之前。本体自足。由其体之如是而及其祛私。方见无所蔽而无不周也。盖字上其理之本具(止)彊为也则大公贯通。理得用形。至于天地万物认作吾仁。然后言其理之本具。则其理者爱之之理耶。万物之理耶。盖字下爱之理(止)后存也者。自有原本体性。自为克己尽后浑全昭著之主。不是大公用行以后事也。正所以辨破盖字上说也。至于此数句云云。上注则统指己私既克(止)非彊为之也。下注则专指己私既克(止)形于外也。而语意自有该摄。不须疑也。且各条更乞详之云。凡五见。而每于起头处。必曰来说云云。其下以己意辨之。然后以更乞详之勘结。未有只录本语而即以此承之。若果是南轩解说己意。爱之理便是仁下。又云二段。何不少举盖字下解中语。以言差紊之故也。此尤见其不然也。自少窃闻野翁之风。知得纯资笃行之大槩。未及亲身禀质。又未得攀阅其师友讲磨之馀论。未遂执鞭之愿。而递有绝弦之叹。奉玩此段甲乙之辨。可想其看文节度。而
字上己私既克(止)非吾仁则体无所具。而直待公后。遽有贯通之妙。到了此后。方得爱之理云。而盖字下皇皇四达(止)仁之用无不周者。既言仁体与天理则有蔽无蔽之前。本体自足。由其体之如是而及其祛私。方见无所蔽而无不周也。盖字上其理之本具(止)彊为也则大公贯通。理得用形。至于天地万物认作吾仁。然后言其理之本具。则其理者爱之之理耶。万物之理耶。盖字下爱之理(止)后存也者。自有原本体性。自为克己尽后浑全昭著之主。不是大公用行以后事也。正所以辨破盖字上说也。至于此数句云云。上注则统指己私既克(止)非彊为之也。下注则专指己私既克(止)形于外也。而语意自有该摄。不须疑也。且各条更乞详之云。凡五见。而每于起头处。必曰来说云云。其下以己意辨之。然后以更乞详之勘结。未有只录本语而即以此承之。若果是南轩解说己意。爱之理便是仁下。又云二段。何不少举盖字下解中语。以言差紊之故也。此尤见其不然也。自少窃闻野翁之风。知得纯资笃行之大槩。未及亲身禀质。又未得攀阅其师友讲磨之馀论。未遂执鞭之愿。而递有绝弦之叹。奉玩此段甲乙之辨。可想其看文节度。而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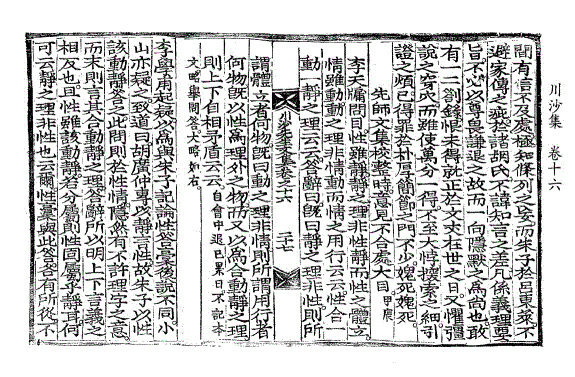 间有信不及处。极知条列之妄。而朱子于吕东莱。不避家传之疵。于诸胡氏。不讳知言之差。凡系义理要旨。不必以尊畏谦退之故而一向隐默之为尚也。敢有一二劄录。恨未得就正于文丈在世之日。又惧彊说之穿穴。而虽使万分一得。不至大悖。探索之细。引證之烦。已得罪于朴厚简节之门不少。愧死愧死。
间有信不及处。极知条列之妄。而朱子于吕东莱。不避家传之疵。于诸胡氏。不讳知言之差。凡系义理要旨。不必以尊畏谦退之故而一向隐默之为尚也。敢有一二劄录。恨未得就正于文丈在世之日。又惧彊说之穿穴。而虽使万分一得。不至大悖。探索之细。引證之烦。已得罪于朴厚简节之门不少。愧死愧死。先师文集校整时。意见不合处大目。(甲辰)
李天牖问目。性虽静。静之理非性静而性之体立。情虽动。动之理非情动而情之用行云云。性合一动一静之理云云。答辞曰。既曰静之理非性。则所谓体立者何物。既曰动之理非情。则所谓用行者何物。既以性为理外之物。而又以为合动静之理。则上下自相矛盾云云。(自会中退已累日。不记本文。略举问答。大略如右。)
李学甫起疑。以为与朱子记论性答稿后说不同。小山亦疑之。致道曰。胡广仲专以静言性。故朱子以性该动静答之。此问则于性情。隐然有不许理字之意。而末则言其合动静之理。答辞所以明上下言义之相反也。且性虽该动静。若分属则性固属乎静耳。何可云静之理非性也云尔。性稿与此答。各有所从。不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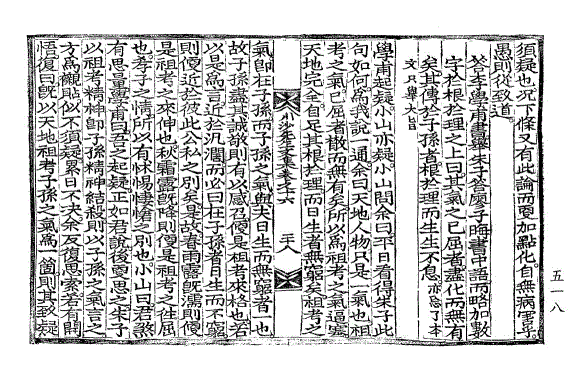 须疑也。况下条又有此论而更加点化。自无病害乎。愚则从致道。
须疑也。况下条又有此论而更加点化。自无病害乎。愚则从致道。答李学甫书。举朱子答廖子晦书中语。而略加数字于根于理之上曰。其气之已屈者。尽化而无有矣。其传于子孙者。根于理而生生不息。(亦忘了本文只举大旨)
学甫起疑。小山亦疑。小山问余曰。平日看得朱子此句如何。为我说一通。余曰。天地人物。只是一气也。祖考之气。已屈者散而无有矣。所以为祖考之气逼塞。天地完全。自足其根于理。而日生者无穷矣。祖考之气。即在子孙。而子孙之气。与夫日生而无穷者一也。故子孙尽其诚敬则有以感召。便是祖考来格也。若以是为言。近于汎阔。而必曰在子孙者日生而不穷。则便近于彼此公私之别矣。是故。春雨露既濡则便是祖考之来伸也。秋霜露既降则便是祖考之往屈也。孝子之情。所以有怵惕悽怆之别也。小山曰。君煞有思量。学甫曰。吾之起疑。正如君说。后更思之。朱子以祖考精神即子孙精神结杀。则以子孙之气言之。方为衬贴。似不须疑。累日不决。余反复思索。若有开悟。复曰。既以天地祖考子孙之气为一个。则其致疑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9H 页
 于在子孙一句者。便有彼此之病。一也。朱子此书。专从子孙之感召祖考为说。结句以祖考子孙。妆杀其气之传于子孙。生生而不穷者。即天地之气根于理而日生不穷也。从子孙为说。通贯本书首尾之义。恐无可疑。学甫可之。小山默然。
于在子孙一句者。便有彼此之病。一也。朱子此书。专从子孙之感召祖考为说。结句以祖考子孙。妆杀其气之传于子孙。生生而不穷者。即天地之气根于理而日生不穷也。从子孙为说。通贯本书首尾之义。恐无可疑。学甫可之。小山默然。昔年略有议论。而今按语类。问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无穷。此是说天地气化之气否。曰。此气只一般。周礼所谓天神地祇人鬼。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说。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自有浩然日生不穷。
答李学甫问。朝祖若以魂帛代柩。则魂帛置席上北向。前设奠。
柳叔远曰。既以魂帛代柩则以魂帛视柩。以奠视魂帛。依前东向。若奠在魂前则子孙之拜辞祖先。祖先无奠。而子孙御食于前。情理未安。近世朴南溪,尹明斋皆主东向。如何。余曰。此是精微处。难以言也。奠之随魂帛者。非为饷馈而别具也。只是魂神依托于此。与魂帛为一体。不可相离而与之相随。奠与魂帛。不可二以看也。岂以不设于祖考而独设于魂帛。为未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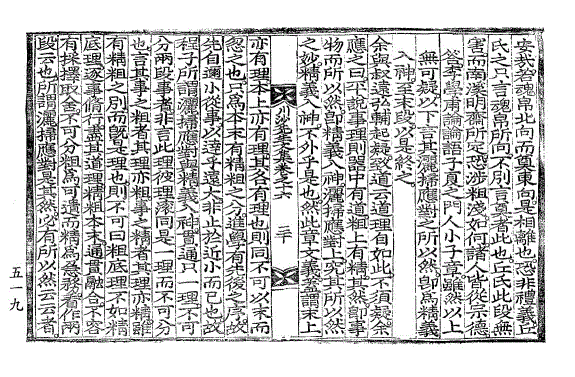 安哉。若魂帛北向而奠东向。是相离也。恐非礼义。丘氏之只言魂帛所向。不别言奠者此也。丘氏此段无害。而南溪,明斋所定。恐涉粗浅。如何。诸人皆从宗德。
安哉。若魂帛北向而奠东向。是相离也。恐非礼义。丘氏之只言魂帛所向。不别言奠者此也。丘氏此段无害。而南溪,明斋所定。恐涉粗浅。如何。诸人皆从宗德。答。李学甫论论语子夏之门人小子章。虽然以上无可疑。以下言其洒扫应对之所以然。即为精义入神。至末段。以是终之。
余与叔远,弘辅起疑。致道云道理自如此。不须疑。余应之曰。平说事理则器中有道。粗上有精。其然。即事物而所以然。即精义入神。洒扫应对上。究其所以然之妙。精义入神。不外乎是也。然此章文义。盖谓末上亦有理。本上亦有理。其各有理也则同。不可以末而忽之也。只为本末有精粗之分。进学有先后之序。故先自迩小从事。以达乎远大。非止于近小而已也。故程子所谓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不可分两段事者。非言此理彼理滚同是一理而不可分也。言其事之粗者其理亦粗。事之精者其理亦精。虽有精粗之别。而既是理也。则不可曰粗底理不如精底理。逐事脩行。尽其道理。精粗本末。通贯融合。不容有采择取舍。不可分粗为可遗而精为急务。看作两段云也。所谓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云云者。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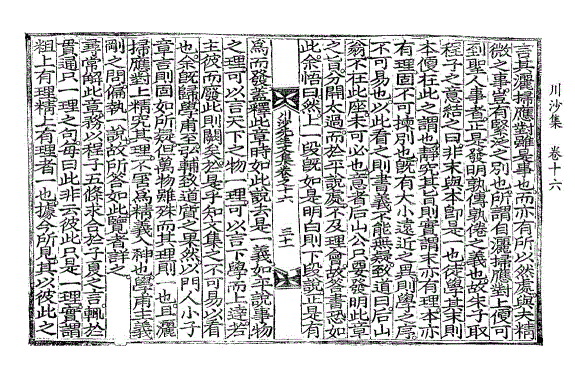 言其洒扫应对虽是事也。而亦有所以然处。与夫精微之事。岂有紧泛之别也。所谓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者。正是发明孰传孰倦之义也。故朱子取程子之意结之曰。非末与本即是一也。徒学其末则本便在此之谓也。静究其旨则实谓末亦有理。本亦有理。固不可拣别也。既有大小远近之异。则学之序。不可易也。以此看之则书义不能无疑。致道曰。后山翁不在此座。未可必也。意者后山公只要发明此章之旨。分开太过。而于平说处。不及理会。故答书恐如此。余悟曰。然。上一段既如是明白则下段说。正是有为而发。盖释此章时。如此说去是一义。如平说事物之理。可以言天下之物一理。可以言下学而上达。若主彼而废此则阙矣。于是乎知文集之不可易以看也。余既归。学甫至。弘辅,致道质之果然。以门人小子章言则固如所疑。但万物虽殊而其理则一也。且洒扫应对上精究其理。不害为精义入神也。学甫主义刚之问。偏执一说。故所答如此。览者详之。
言其洒扫应对虽是事也。而亦有所以然处。与夫精微之事。岂有紧泛之别也。所谓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者。正是发明孰传孰倦之义也。故朱子取程子之意结之曰。非末与本即是一也。徒学其末则本便在此之谓也。静究其旨则实谓末亦有理。本亦有理。固不可拣别也。既有大小远近之异。则学之序。不可易也。以此看之则书义不能无疑。致道曰。后山翁不在此座。未可必也。意者后山公只要发明此章之旨。分开太过。而于平说处。不及理会。故答书恐如此。余悟曰。然。上一段既如是明白则下段说。正是有为而发。盖释此章时。如此说去是一义。如平说事物之理。可以言天下之物一理。可以言下学而上达。若主彼而废此则阙矣。于是乎知文集之不可易以看也。余既归。学甫至。弘辅,致道质之果然。以门人小子章言则固如所疑。但万物虽殊而其理则一也。且洒扫应对上精究其理。不害为精义入神也。学甫主义刚之问。偏执一说。故所答如此。览者详之。寻常解此章。务以程子五条求合于子夏之言。辄于贯通只一理之句。每曰此非云彼此只是一理。实谓粗上有理。精上有理者一也。据今所见。其以彼此之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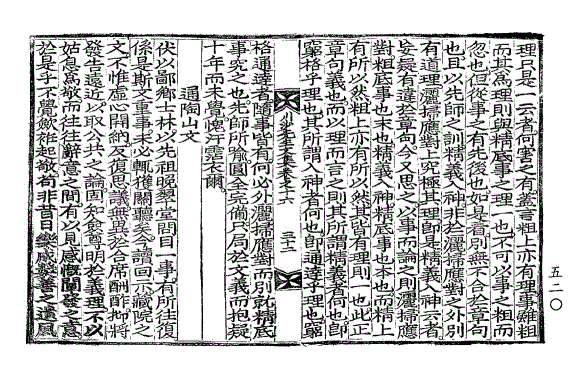 理只是一云者。何害之有。盖言粗上亦有理。事虽粗而其为理则与精底事之理一也。不可以事之粗而忽也。但从事之有先后也。如是看。别无不合于章句也。且以先师之训。精义入神。非于洒扫应对之外别有道理。洒扫应对上究极其理。即是精义入神云者。妄疑有违于章句。今又思之。以事而论之则洒扫应对。粗底事也末也。精义入神。精底事也本也。而精上有所以然。粗上亦有所以然。其皆有理则一也。此正章句义也。而以理而言之则其所谓精义者何也。即穷格乎理也。其所谓入神者何也。即通达乎理也。穷格通达者。随事皆有。何必外洒扫应对而别就精底事究之也。先师所喻。圆全完备。只局于文义。而抱疑十年而未觉。愧汗沾衣尔。
理只是一云者。何害之有。盖言粗上亦有理。事虽粗而其为理则与精底事之理一也。不可以事之粗而忽也。但从事之有先后也。如是看。别无不合于章句也。且以先师之训。精义入神。非于洒扫应对之外别有道理。洒扫应对上究极其理。即是精义入神云者。妄疑有违于章句。今又思之。以事而论之则洒扫应对。粗底事也末也。精义入神。精底事也本也。而精上有所以然。粗上亦有所以然。其皆有理则一也。此正章句义也。而以理而言之则其所谓精义者何也。即穷格乎理也。其所谓入神者何也。即通达乎理也。穷格通达者。随事皆有。何必外洒扫应对而别就精底事究之也。先师所喻。圆全完备。只局于文义。而抱疑十年而未觉。愧汗沾衣尔。通陶山文
伏以鄙乡士林。以先祖晚翠堂问目一事。有所往复。系是斯文重事。未必辄获关听矣。今读回示。藏院之文。不惟虚心开纳。反复思议。无异于合席酬酢。抑将发告远近。以取公共之论。固知佥尊明于义理。不以姑息为敬。而往往辞意之间。有以见感慨阐发之意。于是乎不觉敛衽起敬。苟非昔日乐成奖善之遗风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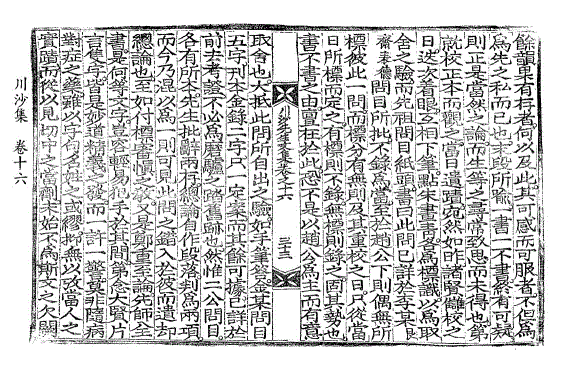 馀韵果有存者。何以及此。其可感而可服者。不但为为先之私而已也。末段所喻。一书一不书。终有可疑。则正是当然之论。而生等之寻常致思而未得也。第就校正本而观之。当日遗迹。宛然如昨。诸贤雠校之日。迭次着眼。互相下笔。点朱画青。各为标识。以为取舍之验。而先祖问目纸头。书曰此问已详于李某(艮斋表德)问目所批。不录为当。至于赵公下则偶无所标彼此一问。而标分有无则及其重校之日。只从当日所标而定之。有标则不录。无标则录之。固其势也。书不书之由。亶在于此。恐不是以赵公为主而有意取舍也。大抵此问所自出之验。如手笔答。金某问目五字。刊本金录二字。只一定案。而其馀可据。已详于前去考證。不必为磨驴之踏旧迹也。然惟二公问目。各有所本。先生批辞两存。总论自作段落。判为两项。而今乃混以为一则可见此问之错入于彼而遗却总论也。至如付标审慎之教。又是郑重至论。先师全书。是何等文字。岂容轻易犯手于其间。第念大贤片言只字。皆是妙道精义之发。而一许一警。莫非随病对症之药。虽以字句名姓之或缪。抑无以考当人之实迹。而从以见切中之当剂。未始不为斯文之欠阙
馀韵果有存者。何以及此。其可感而可服者。不但为为先之私而已也。末段所喻。一书一不书。终有可疑。则正是当然之论。而生等之寻常致思而未得也。第就校正本而观之。当日遗迹。宛然如昨。诸贤雠校之日。迭次着眼。互相下笔。点朱画青。各为标识。以为取舍之验。而先祖问目纸头。书曰此问已详于李某(艮斋表德)问目所批。不录为当。至于赵公下则偶无所标彼此一问。而标分有无则及其重校之日。只从当日所标而定之。有标则不录。无标则录之。固其势也。书不书之由。亶在于此。恐不是以赵公为主而有意取舍也。大抵此问所自出之验。如手笔答。金某问目五字。刊本金录二字。只一定案。而其馀可据。已详于前去考證。不必为磨驴之踏旧迹也。然惟二公问目。各有所本。先生批辞两存。总论自作段落。判为两项。而今乃混以为一则可见此问之错入于彼而遗却总论也。至如付标审慎之教。又是郑重至论。先师全书。是何等文字。岂容轻易犯手于其间。第念大贤片言只字。皆是妙道精义之发。而一许一警。莫非随病对症之药。虽以字句名姓之或缪。抑无以考当人之实迹。而从以见切中之当剂。未始不为斯文之欠阙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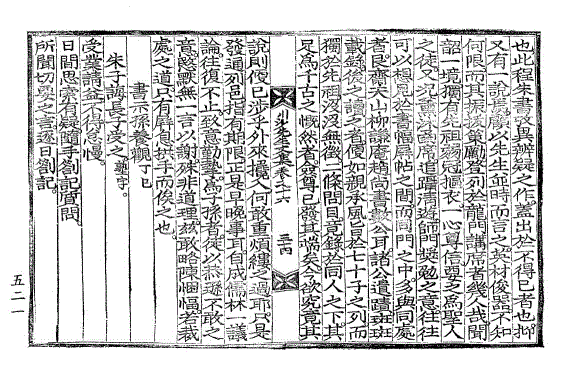 也。此程朱书考异辨疑之作。盖出于不得已者也。抑又有一说焉。顾以先生并时而言之。英材俊器。不知何限。而其振拔策励。登列于龙门讲席者几人哉。闻韶一境。独有先祖弱冠抠衣。一心尊信。要之为圣人之徒。又况薰沐函席。追蹑清游。师门奖勉之意。往往可以想见于书幅屏帖之间。而同门之中。多与同处者。艮斋,天山,柳谦庵,赵尚书数公耳。诸公遗迹。斑斑载录。后之读之者。便如亲承风旨于七十子之列。而独于先祖。没没无徵。二条问目。竟录于同人之下。其足为千古之慨然者。佥尊已发其端矣。今欲究竟其说则便已涉乎外来搀入。何敢重烦缕之过耶。只是发通列邑。指有期限。正是早晚事耳。自成儒林一议论。往复不止。致意勤挚。为子孙者。徒以恭逊不敢之意。悯默无一言以谢。殊非道理。玆敢略陈悃愊。若裁处之道。只有屏息拱手而俟之也。
也。此程朱书考异辨疑之作。盖出于不得已者也。抑又有一说焉。顾以先生并时而言之。英材俊器。不知何限。而其振拔策励。登列于龙门讲席者几人哉。闻韶一境。独有先祖弱冠抠衣。一心尊信。要之为圣人之徒。又况薰沐函席。追蹑清游。师门奖勉之意。往往可以想见于书幅屏帖之间。而同门之中。多与同处者。艮斋,天山,柳谦庵,赵尚书数公耳。诸公遗迹。斑斑载录。后之读之者。便如亲承风旨于七十子之列。而独于先祖。没没无徵。二条问目。竟录于同人之下。其足为千古之慨然者。佥尊已发其端矣。今欲究竟其说则便已涉乎外来搀入。何敢重烦缕之过耶。只是发通列邑。指有期限。正是早晚事耳。自成儒林一议论。往复不止。致意勤挚。为子孙者。徒以恭逊不敢之意。悯默无一言以谢。殊非道理。玆敢略陈悃愊。若裁处之道。只有屏息拱手而俟之也。书示孙养观(丁巳)
朱子诲长子受之。(塾字。)
受业请益。不得怠慢。
日间思索有疑。随手劄记质问。
所闻切要之言。逐日劄记。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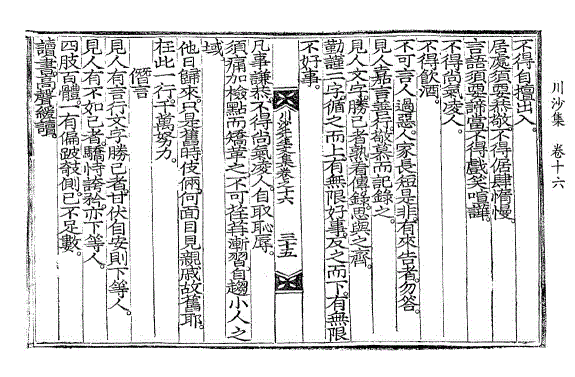 不得自擅出入。
不得自擅出入。居处须要恭敬。不得倨肆惰慢。
言语须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
不得尚气凌人。
不得饮酒。
不可言人过恶。人家长短是非。有来告者。勿答。
见人嘉言善行。敬慕而记录之。
见人文字。胜己者熟看传录。思与之齐。
勤谨二字。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
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
须痛加检点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趋小人之域。
他日归来。只是旧时伎俩。何面目见亲戚故旧耶。
在此一行。千万努力。
僭言
见人有言行文字胜己者。甘伏自安则下等人。
见人有不如己者。骄恃誇矜。亦下等人。
四肢百体。一有偏跛攲侧。已不足数。
读书。高声缓读。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第 522L 页
 读书声。昏沉懒惰不可。浮扬叫唤亦不好。
读书声。昏沉懒惰不可。浮扬叫唤亦不好。读书有味。然后方进。潜心熟读。然后味生。
无间断作撤。则从容优游可以成。有间断作撤。则往往劫督无益。
持心则以不若人为耻。待人则以百不知自处。百不能自退。
持身则重似泰山。事长如口转舌。待人则自虚自谦。勤谨者。不但学进。家事亦周密。有言当干。不暇勉学者。家务亦废。
古人稍稍称名者。皆庄重人。不然。虽有文艺。只是下流。
各坐戏慢尚不可。
文会便是礼席。
一人放纵。满堂蒙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