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x 页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杂著
杂著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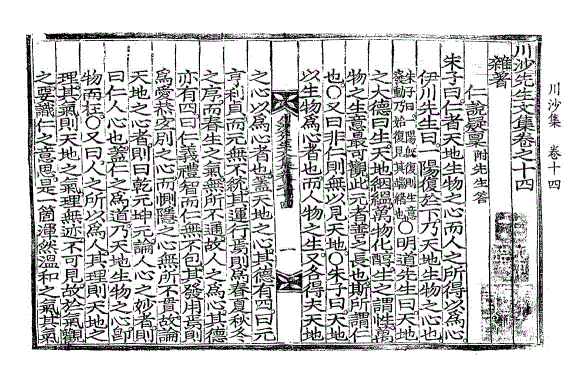 仁说疑禀(附先生答)
仁说疑禀(附先生答)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
伊川先生曰。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朱子曰。一阳既复则生意发动。乃始复见其端绪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又曰非仁则无以见天地。○朱子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心。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又曰。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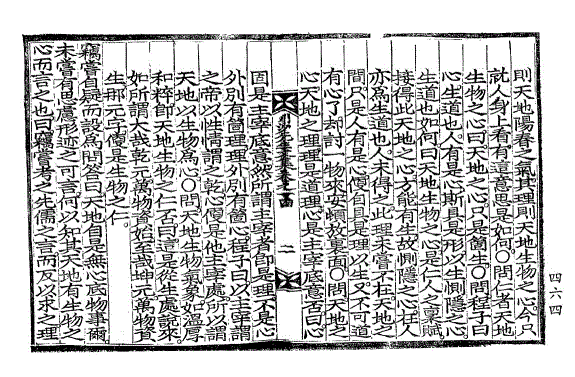 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个生。○问。程子曰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道也。人未得之。此理未尝不在。天地之间。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讨一物来。安顿放里面。○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心便是他主宰处。所以谓天地以生物为心。○问。天地生物气象。如温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这是从生处说来。如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
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个生。○问。程子曰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恻隐之心。生道也如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道也。人未得之。此理未尝不在。天地之间。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讨一物来。安顿放里面。○问。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心便是他主宰处。所以谓天地以生物为心。○问。天地生物气象。如温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这是从生处说来。如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窃尝自疑而设为问答曰。天地自是无心底物事尔。未尝有思虑形迹之可言。何以知其天地有生物之心而言之也。曰。窃尝考之先儒之言。而反以求之。理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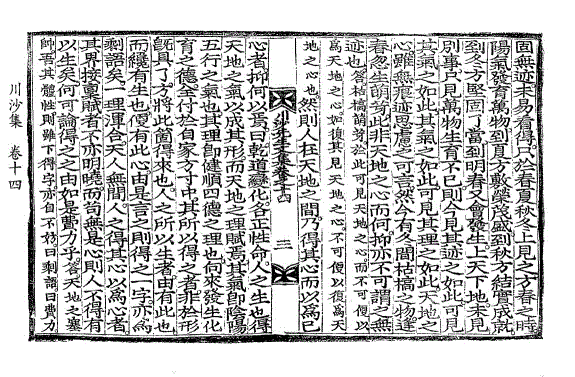 固无迹。未易看得。只于春夏秋冬上见之。方春之时。阳气发育万物。到夏方敷荣茂盛。到秋方结实成就。到冬方坚固了当。到明春又会发生。上天下地。未见别事。只见万物生育不已。则今见其迹之如此。可见其气之如此。其气之如此。可见其理之如此。天地之心。虽无痕迹思虑之可言。然今有冬间枯槁之物。逢春忽生萌芽。此非天地之心而何。抑亦不可谓之无迹也。(答。枯槁萌芽。于此可见天地之心。而不可便以为天地之心。如复其见天地之心。不可便以复为天地之心也。)然则人在天地之间。乃得其心而以为己心者。抑何以焉。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气以成其形。而天地之理赋焉。其气即阴阳五行之气也。其理即健顺四德之理也。向来发生化育之德。全付于自家方寸中。其所以得之者。非于形既具了。方将此个得来也。人之所以生者。由有此也。而才有生也。便有此心。由是言之则得之一字。亦为剩语矣。一理浑合。天人无间。人之得其心以为心者。其界接禀赋者不亦明晓。而苟无是心则人不得有以生矣。何可论得之之由如是费力乎。(答。天地之塞帅。吾其体性。则虽下得字。亦自不妨。曰剩语。曰费力。
固无迹。未易看得。只于春夏秋冬上见之。方春之时。阳气发育万物。到夏方敷荣茂盛。到秋方结实成就。到冬方坚固了当。到明春又会发生。上天下地。未见别事。只见万物生育不已。则今见其迹之如此。可见其气之如此。其气之如此。可见其理之如此。天地之心。虽无痕迹思虑之可言。然今有冬间枯槁之物。逢春忽生萌芽。此非天地之心而何。抑亦不可谓之无迹也。(答。枯槁萌芽。于此可见天地之心。而不可便以为天地之心。如复其见天地之心。不可便以复为天地之心也。)然则人在天地之间。乃得其心而以为己心者。抑何以焉。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气以成其形。而天地之理赋焉。其气即阴阳五行之气也。其理即健顺四德之理也。向来发生化育之德。全付于自家方寸中。其所以得之者。非于形既具了。方将此个得来也。人之所以生者。由有此也。而才有生也。便有此心。由是言之则得之一字。亦为剩语矣。一理浑合。天人无间。人之得其心以为心者。其界接禀赋者不亦明晓。而苟无是心则人不得有以生矣。何可论得之之由如是费力乎。(答。天地之塞帅。吾其体性。则虽下得字。亦自不妨。曰剩语。曰费力。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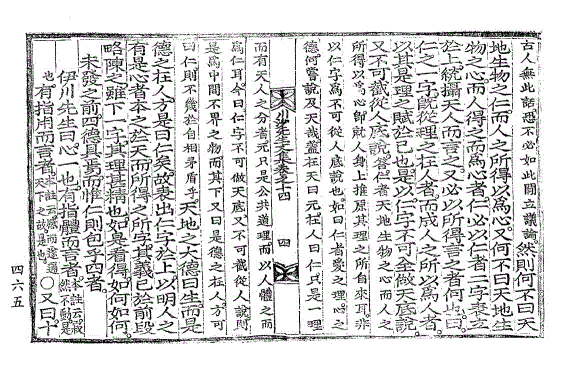 古人无此话。恐不必如此閒立议论。)然则何不曰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得以为心。又何不曰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而为心者。仁必以仁者二字表立于上。统摄天人而言之。又必以所得言之者何也。曰。仁之一字。既从理之在人者。而成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是理之赋于己也。是以。仁字不可全做天底说。又不可截从人底说。(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即就人身上推原其理之所自来耳。非以仁字为不可从人底说也。如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何尝说及天哉。盖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只是一理而有天人之分者。元只是公共道理。而以人体之而为仁耳。今曰。仁字不可做天底。又不可截从人说。则是为中间不界之物。而其下又曰是德之在人。方可曰仁。则不几于自相矛盾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是德之在人。方是曰仁矣。故表出仁字于上。以明人之有是心者本之于天。而所得之所字。其义已于前段略陈之。虽下一字。其理甚精也。如是看得。如何如何。
古人无此话。恐不必如此閒立议论。)然则何不曰天地生物之仁。而人之所得以为心。又何不曰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而为心者。仁必以仁者二字表立于上。统摄天人而言之。又必以所得言之者何也。曰。仁之一字。既从理之在人者。而成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是理之赋于己也。是以。仁字不可全做天底说。又不可截从人底说。(答。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即就人身上推原其理之所自来耳。非以仁字为不可从人底说也。如曰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何尝说及天哉。盖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只是一理而有天人之分者。元只是公共道理。而以人体之而为仁耳。今曰。仁字不可做天底。又不可截从人说。则是为中间不界之物。而其下又曰是德之在人。方可曰仁。则不几于自相矛盾乎。)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是德之在人。方是曰仁矣。故表出仁字于上。以明人之有是心者本之于天。而所得之所字。其义已于前段略陈之。虽下一字。其理甚精也。如是看得。如何如何。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
伊川先生曰。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又曰。十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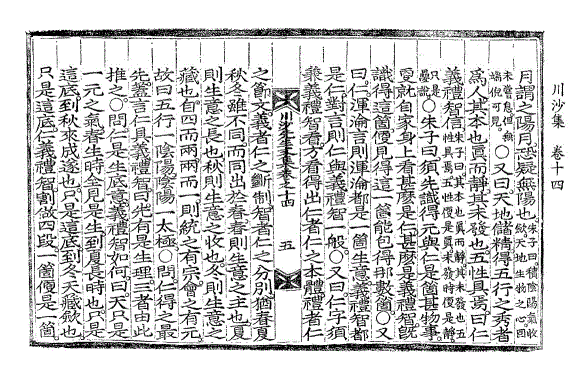 月谓之阳月。恐疑无阳也。(朱子曰。积阴阳气收敛。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又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朱子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发时便是静。只是叠说。)○朱子曰。须先识得元与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么是仁。甚么是义礼智。既识得这个。便见得这一个能包得那数个。○又曰。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又曰。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主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收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问。仁得之最先。盖言仁具义礼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
月谓之阳月。恐疑无阳也。(朱子曰。积阴阳气收敛。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尝息。但无端倪可见。)○又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朱子曰。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五性便是真。未发时便是静。只是叠说。)○朱子曰。须先识得元与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么是仁。甚么是义礼智。既识得这个。便见得这一个能包得那数个。○又曰。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又曰。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主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收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问。仁得之最先。盖言仁具义礼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6L 页
 浑沦看只是一个。○问。仁是统体底否。曰。且理会义礼智令分明。其空阙一处便是仁。○问。仁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又问先生语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西山真氏曰。心之德。何也。盖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则得于天。仁义礼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贞皆乾之德。而元独为四德之长。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为天之全德。故仁亦为人之全德。
浑沦看只是一个。○问。仁是统体底否。曰。且理会义礼智令分明。其空阙一处便是仁。○问。仁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又问先生语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西山真氏曰。心之德。何也。盖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则得于天。仁义礼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贞皆乾之德。而元独为四德之长。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为天之全德。故仁亦为人之全德。问。未发之前只是性也。性则一而已矣。何以见其有四者之具。而仁又包得其三者焉。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其动静屈伸之间。自有始终微盛之渐。故于是开成四片。如元亨利贞之各得其名位。实有若分间架。条目井井。元者自是生之理也。亨者自是通之理也。利者成之理也。贞者藏之理也。有不可把亨作元。把利作贞。然其所谓生长成遂者。只是曰一个元也。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也。人之生也。得其阴与阳也。而斯有健顺之德。得其元亨与利贞也。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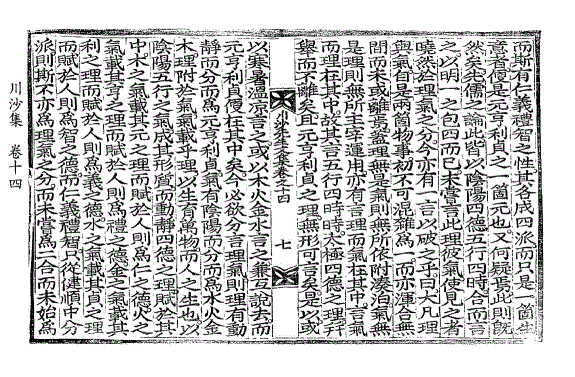 而斯有仁义礼智之性。其各成四派。而只是一个生意者。便是元亨利贞之一个元也。又何疑焉。此则既然矣。先儒之论此。皆以阴阳四德五行四时。合而言之。以明一之包四而已。未尝言此理彼气。使见之者晓然于理气之分。今亦有一言以破之乎。曰。大凡理与气。自是两个物事。初不可混杂为一。而亦浑合无间而未或离焉。盖理无是气则无所依附凑泊。气无是理则无所主宰运用。亦有言理而气在其中。言气而理在其中。故其言五行四时时。太极四德之理。并举而不离矣。且元亨利贞之理。无形可言矣。是以。或以寒暑温凉言之。或以木火金水言之。兼互说去。而元亨利贞便在其中矣。今必欲分言理气。则理有动静而分而为元亨利贞。气有阴阳而分而为水火金木。理附于气。气载乎理。以生育万物。而人之生也。以阴阳五行之气。成其形质。而动静四德之理。赋于其中。木之气载其元之理而赋于人则为仁之德。火之气载其亨之理而赋于人则为礼之德。金之气载其利之理而赋于人则为义之德。水之气载其贞之理而赋于人则为智之德。而仁义礼智。只从健顺中分派。则斯不亦为理气之分。而未尝为二合而未始为
而斯有仁义礼智之性。其各成四派。而只是一个生意者。便是元亨利贞之一个元也。又何疑焉。此则既然矣。先儒之论此。皆以阴阳四德五行四时。合而言之。以明一之包四而已。未尝言此理彼气。使见之者晓然于理气之分。今亦有一言以破之乎。曰。大凡理与气。自是两个物事。初不可混杂为一。而亦浑合无间而未或离焉。盖理无是气则无所依附凑泊。气无是理则无所主宰运用。亦有言理而气在其中。言气而理在其中。故其言五行四时时。太极四德之理。并举而不离矣。且元亨利贞之理。无形可言矣。是以。或以寒暑温凉言之。或以木火金水言之。兼互说去。而元亨利贞便在其中矣。今必欲分言理气。则理有动静而分而为元亨利贞。气有阴阳而分而为水火金木。理附于气。气载乎理。以生育万物。而人之生也。以阴阳五行之气。成其形质。而动静四德之理。赋于其中。木之气载其元之理而赋于人则为仁之德。火之气载其亨之理而赋于人则为礼之德。金之气载其利之理而赋于人则为义之德。水之气载其贞之理而赋于人则为智之德。而仁义礼智。只从健顺中分派。则斯不亦为理气之分。而未尝为二合而未始为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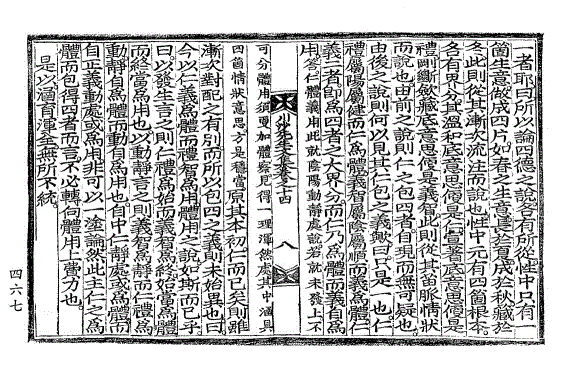 一者耶。曰。所以论四德之说。各有所从。性中只有一个生意。做成四片。如春之生意。长于夏。成于秋。藏于冬。此则从其渐次流注而说也。性中元有四个根本。各有界分。其温和底意思便是仁。宣著底意思便是礼。刚断敛藏底意思便是义智。此则从其苗脉情状而说也。由前之说则仁之包四者。自现而无可疑也。由后之说则何以见其仁包之义欤。曰。只是一也。仁礼属阳属健而仁为体。义智属阴属顺而义为体。仁义二者。即为四者之大界分。而仁乃为体而义自为用。(答。仁体义用。此就阴阳动静处说。若就未发上。不可分体用。须更加体察。见得一理浑然处。其中涵具四个情状意思。方是稳当。)原其本初。仁而已矣。则虽渐次对配之有别。而所以包四之义则未始异也。曰。今以仁义为体而礼智为用。体用之说。如斯而已乎。曰。以发生言之则仁礼为始而义智为终。始当为体而终当为用也。以动静言之则义智为静而仁礼为动。静自为体而动自为用也。自中仁静处或为体。而自正义动处或为用。非可以一涂论。然此主仁之为体而包得四者而言。不必转向体用上费力也。
一者耶。曰。所以论四德之说。各有所从。性中只有一个生意。做成四片。如春之生意。长于夏。成于秋。藏于冬。此则从其渐次流注而说也。性中元有四个根本。各有界分。其温和底意思便是仁。宣著底意思便是礼。刚断敛藏底意思便是义智。此则从其苗脉情状而说也。由前之说则仁之包四者。自现而无可疑也。由后之说则何以见其仁包之义欤。曰。只是一也。仁礼属阳属健而仁为体。义智属阴属顺而义为体。仁义二者。即为四者之大界分。而仁乃为体而义自为用。(答。仁体义用。此就阴阳动静处说。若就未发上。不可分体用。须更加体察。见得一理浑然处。其中涵具四个情状意思。方是稳当。)原其本初。仁而已矣。则虽渐次对配之有别。而所以包四之义则未始异也。曰。今以仁义为体而礼智为用。体用之说。如斯而已乎。曰。以发生言之则仁礼为始而义智为终。始当为体而终当为用也。以动静言之则义智为静而仁礼为动。静自为体而动自为用也。自中仁静处或为体。而自正义动处或为用。非可以一涂论。然此主仁之为体而包得四者而言。不必转向体用上费力也。是以。涵育浑全。无所不统。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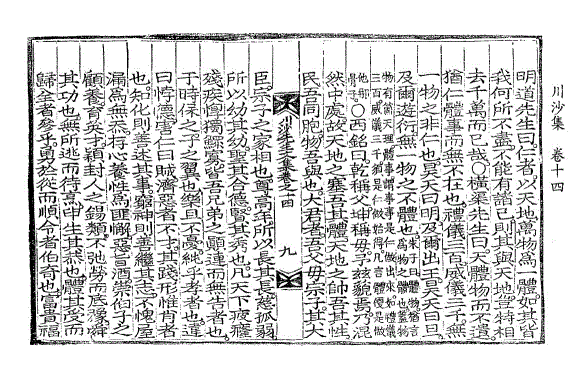 明道先生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诸己。则其与天地。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横渠先生曰。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朱子曰。体物。犹言为物之体也。盖物物有个天理。体事。谓事事是仁做出来。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做他那骨子。)○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
明道先生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如其皆我何所不尽。不能有诸己。则其与天地。岂特相去千万而已哉。○横渠先生曰。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朱子曰。体物。犹言为物之体也。盖物物有个天理。体事。谓事事是仁做出来。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做他那骨子。)○西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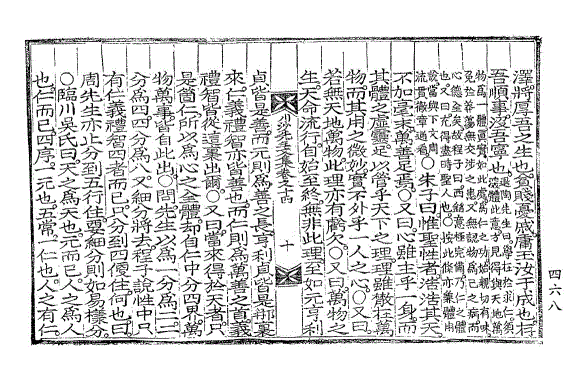 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退陶先生曰。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按此条亦兼体用说。当与下文周流贯彻章通看。)○朱子曰。惟圣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万善足焉。○又曰。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又曰。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又曰。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终。无非此理。至如元亨利贞皆是善。而元则为善之长。亨利贞皆是那里来。仁义礼智亦皆善也。而仁则为万善之首。义礼智皆从这里出尔。○又曰。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万物万事。皆自此出。○问。先生以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又细分将去。程子说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要细分则如易样分。○临川吴氏曰。天之为天也。元而已。人之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
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退陶先生曰。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实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莽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铭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充得尽时圣人也。○按此条亦兼体用说。当与下文周流贯彻章通看。)○朱子曰。惟圣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万善足焉。○又曰。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又曰。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又曰。万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终。无非此理。至如元亨利贞皆是善。而元则为善之长。亨利贞皆是那里来。仁义礼智亦皆善也。而仁则为万善之首。义礼智皆从这里出尔。○又曰。当来得于天者。只是个仁。所以为心之全体。却自仁中分四界。万物万事。皆自此出。○问。先生以为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又细分将去。程子说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要细分则如易样分。○临川吴氏曰。天之为天也。元而已。人之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仁也。人之有仁。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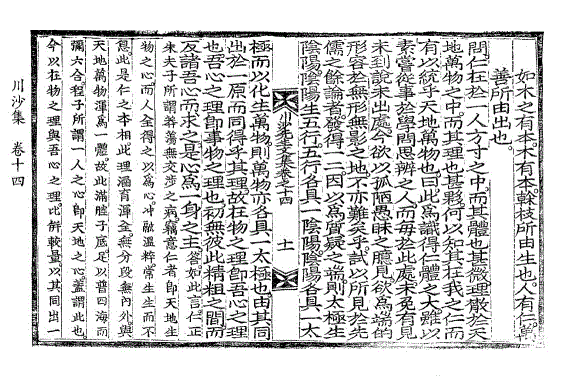 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干枝所由生也。人有仁。万善所由出也。
如木之有本。木有本。干枝所由生也。人有仁。万善所由出也。问。仁在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其体也甚微。理散于天地万物之中。而其理也甚夥。何以知其在我之仁而有以统乎天地万物也。曰。此为识得仁体之大。虽以素尝从事于学问思辨之人。而每于此处。未免有见未到说未出处。今欲以孤陋愚眛之臆见。欲为端的形容于无形无影之地。不亦难矣乎。试以所见于先儒之馀论者。发得一二。因以为质疑之端。则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各具一阴阳。阴阳各具一太极而以化生万物。则万物亦各具一太极也。由其同出于一原而同得乎其理。故在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吾心之理即事物之理也。初无彼此精粗之间。而反诸吾心而求之。是心为一身之主。(答。如此言。仁正朱夫子所谓莽荡无交涉之病。窃意仁者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全得之以为心。冲融温粹。常生生而不息。此是仁之本相。此理涵育浑全。无分段无内外。与天地万物浑为一体。故此满腔子底。足以普四海而弥六合。程子所谓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盖谓此也。今以在物之理与吾心之理。比并较量。以其同出一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69L 页
 原而彊名之曰仁。则恐近于阔疏而不情也。如何。)而未发之前。浑然在中。虚灵不眛。(答。浑然在中。以理言。虚灵不眛。以心言。亦不可夹杂说。)而其体则仁也。实与天地而同其大。天道无外。此心之仁亦无外。天道无限量。此心之仁亦无限量。天道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吾心之仁。凡巨细隐见远近前后。千绪万头。莫不总管辏会于此心之仁。方其静也。虽未见影响之可寻。然苟无其体之无所不统。则何以为万化百行之原。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哉。释氏所以洞见心体。(答。释氏虽瞥见心性影像。而不知真实体面。今许以洞见则亦太恕矣。)而其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只见光辉闪烁。而不知性中包得许多道理。所以求道于运水搬柴之末。而终至于绝伦灭法。重得罪于圣人也。然则既曰万物之理即与吾心之理为一。而仁无不统。则抑可谓仁在万物而少了一物。此理亦有亏欠耶。曰。万物生于太极而亦各具太极。则虽曰仁在万物。未为无理之言。(答。仁是吾心所具之生理。其体足以涵万善。其用足以贯万事。今见万物之各具太极。而谓仁在万物。则所谓仁者。离内而外。舍心
原而彊名之曰仁。则恐近于阔疏而不情也。如何。)而未发之前。浑然在中。虚灵不眛。(答。浑然在中。以理言。虚灵不眛。以心言。亦不可夹杂说。)而其体则仁也。实与天地而同其大。天道无外。此心之仁亦无外。天道无限量。此心之仁亦无限量。天道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无一物之不体。而万物无一之非吾心之仁。凡巨细隐见远近前后。千绪万头。莫不总管辏会于此心之仁。方其静也。虽未见影响之可寻。然苟无其体之无所不统。则何以为万化百行之原。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哉。释氏所以洞见心体。(答。释氏虽瞥见心性影像。而不知真实体面。今许以洞见则亦太恕矣。)而其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只见光辉闪烁。而不知性中包得许多道理。所以求道于运水搬柴之末。而终至于绝伦灭法。重得罪于圣人也。然则既曰万物之理即与吾心之理为一。而仁无不统。则抑可谓仁在万物而少了一物。此理亦有亏欠耶。曰。万物生于太极而亦各具太极。则虽曰仁在万物。未为无理之言。(答。仁是吾心所具之生理。其体足以涵万善。其用足以贯万事。今见万物之各具太极。而谓仁在万物。则所谓仁者。离内而外。舍心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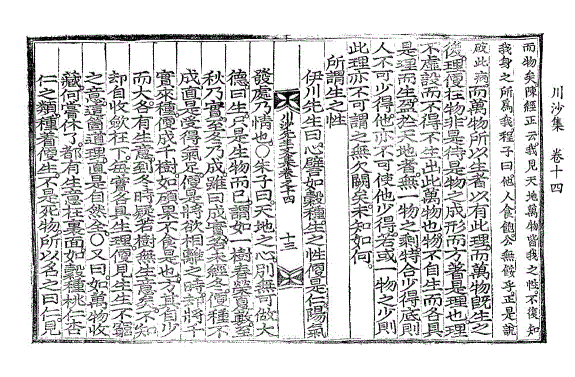 而物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所为我。程子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而万物所以生者以有此理。而万物既生之后。理便在物。非是待是物之成形而方著是理也。理不虚设而不得不生出此万物也。物不自生而各具是理而生。盈于天地者。无一物之剩。特合少得底则人不可少得。他亦不可使他少得。若或一物之少则此理亦不可谓之无欠阙矣。未知如何。
而物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所为我。程子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而万物所以生者以有此理。而万物既生之后。理便在物。非是待是物之成形而方著是理也。理不虚设而不得不生出此万物也。物不自生而各具是理而生。盈于天地者。无一物之剩。特合少得底则人不可少得。他亦不可使他少得。若或一物之少则此理亦不可谓之无欠阙矣。未知如何。所谓生之性
伊川先生曰。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朱子曰。天地之心。别无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谓如一树春荣夏敷。至秋乃实。至冬乃成。虽曰成实。若未经冬。便种不成。直是受得气足。便是将欲相离之时。却将千实来种。便成千树。如硕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少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时疑若树无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敛在下。每实各具生理。便见生生不穷之意。这个道理。直是自然全。○又曰。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谷种桃仁杏仁之类。种着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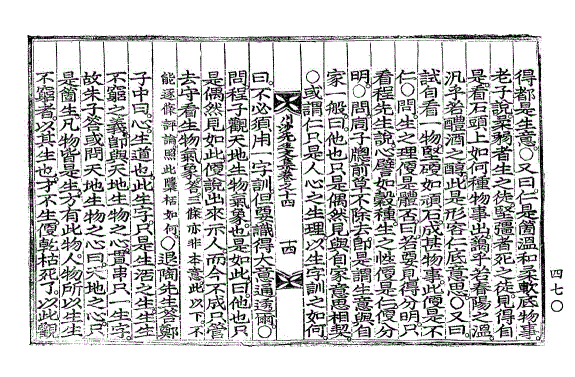 得都是生意。○又曰。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彊者死之徒。见得自是。看石头上如何种物事出。蔼乎若春阳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又曰。试自看一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问。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要见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问。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谓生意与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见与自家意思相契。○或谓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训之如何。曰。不必须用一字训。但要识得大意通透尔。○问。程子观天地生物气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见如此。便说出来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气象。(答。三条亦非本意。此以下。不能逐条评论。照此檃栝如何。)○退陶先生答郑子中曰。心。生道也。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生不穷之义。即与天地生物之心。贯串只一生字。故朱子答或问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以此观
得都是生意。○又曰。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彊者死之徒。见得自是。看石头上如何种物事出。蔼乎若春阳之温。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又曰。试自看一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问。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要见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问。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即是谓生意与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见与自家意思相契。○或谓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训之如何。曰。不必须用一字训。但要识得大意通透尔。○问。程子观天地生物气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见如此。便说出来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气象。(答。三条亦非本意。此以下。不能逐条评论。照此檃栝如何。)○退陶先生答郑子中曰。心。生道也。此生字。只是生活之生。生生不穷之义。即与天地生物之心。贯串只一生字。故朱子答或问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死了。以此观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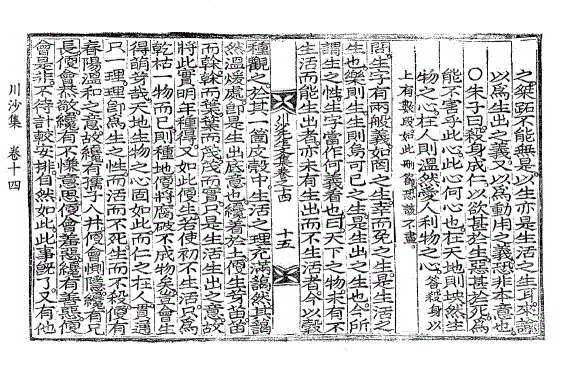 之。桀蹠不能无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耳。来谕以为生出之义。又以为动用之义。恐非本意也。○朱子曰。杀身成仁。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答。杀身以上有数段。如此删节。恐该不尽。)
之。桀蹠不能无是。以生亦是生活之生耳。来谕以为生出之义。又以为动用之义。恐非本意也。○朱子曰。杀身成仁。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答。杀身以上有数段。如此删节。恐该不尽。)问。生字有两般义。如罔之生。幸而免之生。是生活之生也。乐则生。生则乌可已之生。是生出之生也。今所谓生之性。生字当作何义看也。曰。天下之物。未有不生活而能生出者。亦未有生出而不生活者。今以谷种观之。于其一个皮壳中。生活之理充满蔼然。其蔼然温煖处。即是生出底意也。才着于土。便生芽苗。苗而干。干而叶。叶而茂。茂而实。只是生活生出之意。故将此实明年种得。又如此便生。若使初不生活。只为乾枯一物而已。则种地便将腐破不成物矣。岂会生得萌芽哉。天地生物之心固如此。而仁之在人。贯通只一理。理即为生之性。而活而不死。生而不杀。便有春阳温和之意。故才有孺子入井。便会恻隐。才有兄长。便会恭敬。才有不慊意思。便会羞恶。才有善恶。便会是非。不待计较安排。自然如此。此事既了。又有他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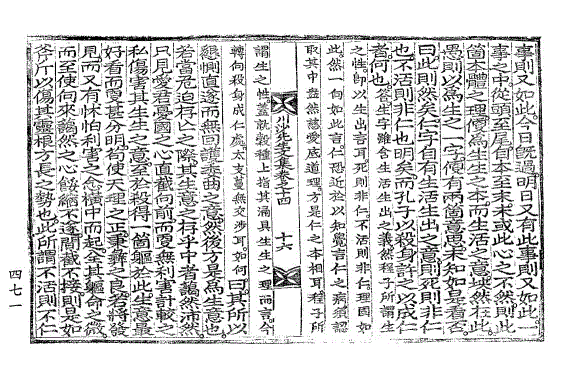 事则又如此。今日既过。明日又有此事则又如此。一事之中。从头至尾。自本至末。未或此心之不然。则此个本体之理。便为生生之本。而生活之意。坱然在此。愚则以为生之一字。便有两个意思。未知如是看否。曰。此则然矣。仁字自有生活生出之意。则死则非仁也。不活则非仁也明矣。而孔子以杀身许之以成仁者。何也。(答。生字虽含生活生出之义。然程子所谓生之性。即以生出言耳。死则非仁。不活则非仁。理固如此。然一向如此言。仁恐近于以知觉言仁之病。须认取其中盎然慈爱底道理。方是仁之本相耳。程子所谓生之性。盖就谷种上指其涵具生生之理而言。今转向杀身成仁处。太支蔓无交涉耳。如何。)曰。其所以恳恻直遂而无回护委曲之意。然后方是为生意也。若当危迫存亡之际。其生意之存乎中者蔼然沛然。只见爱君忧国之心直截向前。而更无利害计较之私伤害其生生之意。至于杀得一个躯于此。生意最好看而更甚分明。苟使天理之正。秉彝之良。若将发见。而又有怵怕利害之念横中而起。全其躯命之微。而至使向来蔼然之心馁缩不遂。间截不接。则是如斧斤以伤其灵根方长之势也。此所谓不活则不仁
事则又如此。今日既过。明日又有此事则又如此。一事之中。从头至尾。自本至末。未或此心之不然。则此个本体之理。便为生生之本。而生活之意。坱然在此。愚则以为生之一字。便有两个意思。未知如是看否。曰。此则然矣。仁字自有生活生出之意。则死则非仁也。不活则非仁也明矣。而孔子以杀身许之以成仁者。何也。(答。生字虽含生活生出之义。然程子所谓生之性。即以生出言耳。死则非仁。不活则非仁。理固如此。然一向如此言。仁恐近于以知觉言仁之病。须认取其中盎然慈爱底道理。方是仁之本相耳。程子所谓生之性。盖就谷种上指其涵具生生之理而言。今转向杀身成仁处。太支蔓无交涉耳。如何。)曰。其所以恳恻直遂而无回护委曲之意。然后方是为生意也。若当危迫存亡之际。其生意之存乎中者蔼然沛然。只见爱君忧国之心直截向前。而更无利害计较之私伤害其生生之意。至于杀得一个躯于此。生意最好看而更甚分明。苟使天理之正。秉彝之良。若将发见。而又有怵怕利害之念横中而起。全其躯命之微。而至使向来蔼然之心馁缩不遂。间截不接。则是如斧斤以伤其灵根方长之势也。此所谓不活则不仁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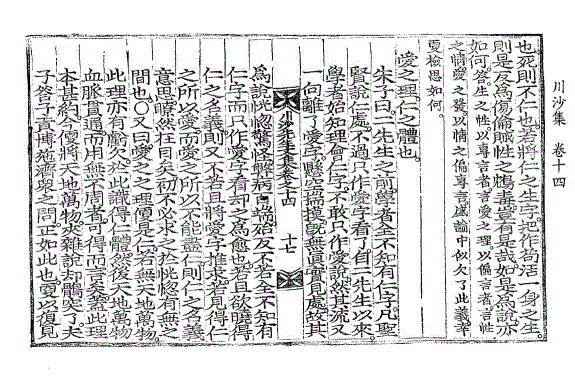 也。死则不仁也。若将仁之生字。把作苟活一身之生。则是反为伤伦贼性之鸩毒。岂有是哉。如是为说。亦如何。(答。生之性。以专言者。言爱之理。以偏言者。言性之情。爱之发。以情之偏专言。盛论中似欠了此义。幸更检思如何。)
也。死则不仁也。若将仁之生字。把作苟活一身之生。则是反为伤伦贼性之鸩毒。岂有是哉。如是为说。亦如何。(答。生之性。以专言者。言爱之理。以偏言者。言性之情。爱之发。以情之偏专言。盛论中似欠了此义。幸更检思如何。)爱之理。仁之体也。
朱子曰。二先生之前。学者全不知有仁字。凡圣贤说仁处。不过只作爱字看了。自二先生以来。学者始知理会仁字。不敢只作爱说。然其流又一向离了爱字。悬空揣摸。既无真实见处。故其为说恍惚惊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爱字看却之为愈也。若且欲晓得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无之间也。○又曰。爱之之理便是仁。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于此识得仁体。然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用无不周者。可得而言矣。盖此理本甚约。今便将天地万物。夹杂说却鹘突了。夫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正如此也。更以复见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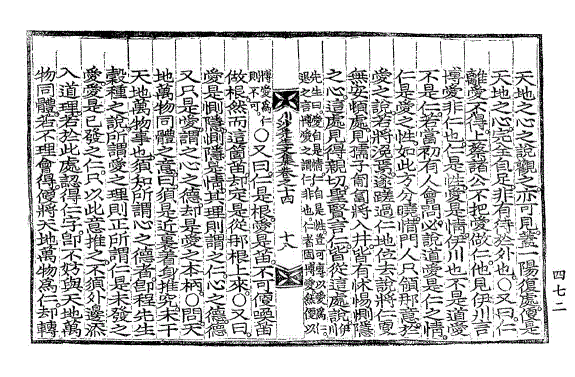 天地之心之说观之。亦可见。盖一阳复处。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于外也。○又曰。仁离爱不得。上蔡诸公不把爱做仁。他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仁是性。爱是情。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惜门人只领那意。于爱之说。若将浼焉。遂蹉过仁地位去说将仁更无安顿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伊川先生曰。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又曰。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又曰。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问。天地万物同体之意。曰。须是近里着身推究。未干天地万物事也。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只以此意推之。不须外边添入道理。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若不理会得。便将天地万物为仁。却转
天地之心之说观之。亦可见。盖一阳复处。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于外也。○又曰。仁离爱不得。上蔡诸公不把爱做仁。他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仁是性。爱是情。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惜门人只领那意。于爱之说。若将浼焉。遂蹉过仁地位去说将仁更无安顿处。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伊川先生曰。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又曰。仁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又曰。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爱。谓之心之德。却是爱之本柄。○问。天地万物同体之意。曰。须是近里着身推究。未干天地万物事也。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只以此意推之。不须外边添入道理。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若不理会得。便将天地万物为仁。却转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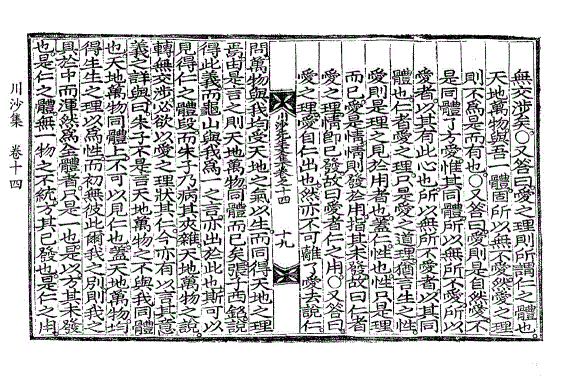 无交涉矣。○又答曰。爱之理则所谓仁之体也。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固所以无不爱。然爱之理则不为是而有也。○又答曰。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惟其同体。所以无所不爱。所以爱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无所不爱者。以其同体也。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又答曰。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
无交涉矣。○又答曰。爱之理则所谓仁之体也。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固所以无不爱。然爱之理则不为是而有也。○又答曰。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惟其同体。所以无所不爱。所以爱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无所不爱者。以其同体也。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又答曰。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问。万物与我均受天地之气以生。而同得天地之理焉。由是言之则天地万物。同体而已矣。张子西铭。说得此义。而龟山与我为一之言。亦出于此也。斯可以见得仁之体段。而朱子乃病其夹杂。天地万物之说。转无交涉。必欲以爱之理状其仁。今亦有以言其意义之详与。曰。朱子不是言天地万物之不与我同体也。天地万物同体上。不可以见仁也。盖天地万物。均得生生之理以为性。而初无彼此尔我之别。则我之具于中而浑然为全体者。只是一也。是以。方其未发也。是仁之体。无一物之不统。方其已发也。是仁之用。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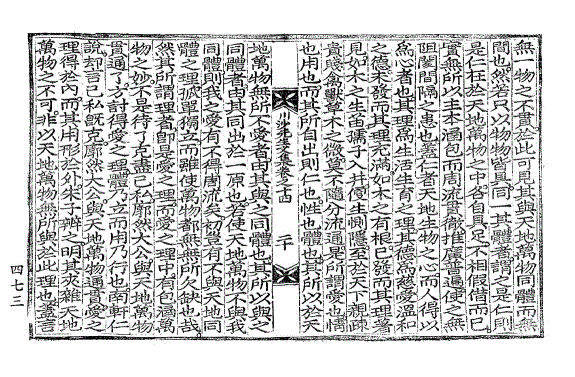 无一物之不贯。于此可见其与天地万物同体而无间也。然若只以物物皆具。同一其体者。谓之是仁则是仁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各自具足。不相假借而已。实无所以主本涵包而周流贯彻。推广普遍。使之无阻阂间隔之患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为心者也。其理为生活生育之理。其德为慈爱温和之德。未发而其理充满。如木之有根。已发而其理著见。如木之生苗。孺子入井。便生恻隐。至于天下亲疏贵贱禽兽草木之微。莫不随分流通。是所谓爱也。情也用也。而其所自出则仁也。性也体也。其所以于天地万物无所不爱者。由其与之同体也。其所以与之同体者。由其同出于一原也。若使天地万物不与我同体。则我之爱有不得周流矣。初岂有不与天地同体之理。孤单独立。而虽使万物都无无所欠缺也哉。然其所谓理者。即是爱之理。而爱之理中。有包涵万物之妙。不是待了克尽己私。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贯通了。方讨得爱之理。体乃立而用乃行也。南轩仁说。却言己私既克。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通贯。爱之理得于内。而其用形于外。朱子辨之。明其夹杂天地万物之不可。非以天地万物无所与于此理也。盖言
无一物之不贯。于此可见其与天地万物同体而无间也。然若只以物物皆具。同一其体者。谓之是仁则是仁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各自具足。不相假借而已。实无所以主本涵包而周流贯彻。推广普遍。使之无阻阂间隔之患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为心者也。其理为生活生育之理。其德为慈爱温和之德。未发而其理充满。如木之有根。已发而其理著见。如木之生苗。孺子入井。便生恻隐。至于天下亲疏贵贱禽兽草木之微。莫不随分流通。是所谓爱也。情也用也。而其所自出则仁也。性也体也。其所以于天地万物无所不爱者。由其与之同体也。其所以与之同体者。由其同出于一原也。若使天地万物不与我同体。则我之爱有不得周流矣。初岂有不与天地同体之理。孤单独立。而虽使万物都无无所欠缺也哉。然其所谓理者。即是爱之理。而爱之理中。有包涵万物之妙。不是待了克尽己私。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贯通了。方讨得爱之理。体乃立而用乃行也。南轩仁说。却言己私既克。廓然大公。与天地万物通贯。爱之理得于内。而其用形于外。朱子辨之。明其夹杂天地万物之不可。非以天地万物无所与于此理也。盖言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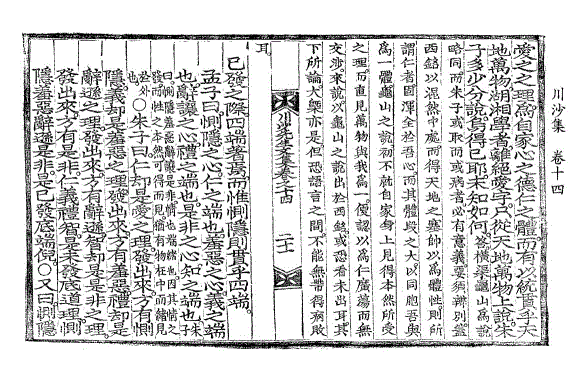 爱之之理。为自家心之德仁之体。而有以统贯乎天地万物。湖湘学者。离绝爱字。只从天地万物上说。朱子多少分说。乌得已耶。未知如何。(答。横渠,龟山为说略同。而朱子或取而或病者。必有意义。要须辨别。盖西铭以混然中处。而得天地之塞帅以为体性。则所谓仁者。固浑全于吾心。而其体段之大。以同胞吾与为一体。龟山之说。初不就自家身上见得本然所受之理。而直见万物与我为一。便认以为仁广荡而无交涉。来说。以龟山之说出于西铭。或恐看未出耳。其下所论。大槩亦是。但恐语言之间。不能无带得病败耳。)
爱之之理。为自家心之德仁之体。而有以统贯乎天地万物。湖湘学者。离绝爱字。只从天地万物上说。朱子多少分说。乌得已耶。未知如何。(答。横渠,龟山为说略同。而朱子或取而或病者。必有意义。要须辨别。盖西铭以混然中处。而得天地之塞帅以为体性。则所谓仁者。固浑全于吾心。而其体段之大。以同胞吾与为一体。龟山之说。初不就自家身上见得本然所受之理。而直见万物与我为一。便认以为仁广荡而无交涉。来说。以龟山之说出于西铭。或恐看未出耳。其下所论。大槩亦是。但恐语言之间。不能无带得病败耳。)已发之际。四端著焉。而惟恻隐则贯乎四端。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朱子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朱子曰。仁却是爱之理。发出来。方有恻隐。义却是羞恶之理。发出来。方有羞恶。礼却是辞逊之理。发出来。方有辞逊。智却是是非之理。发出来。方有是非。仁义礼智。是未发底道理。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是已发底端倪。○又曰。恻隐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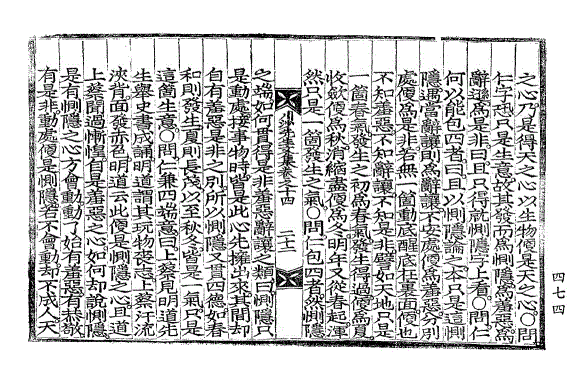 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物便是天之心。○问。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曰。且只得就恻隐字上看。○问。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且以恻隐论之。本只是这恻隐。遇当辞让则为辞让。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让。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个春气。发生之初为春气。发生得过。便为夏。收敛便为秋。消缩尽便为冬。明年又从春起。浑然只是一个发生之气。○问。仁包四者。然恻隐之端。如何贯得是非羞恶辞让之类。曰。恻隐只是动处。接事物时。皆是此心先拥出来。其间却自有羞恶是非之别。所以恻隐又贯四德。如春和则发生。夏则长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气。只是这个生意。○问。仁兼四端意。曰。上蔡见明道先生举史书成诵。明道谓其玩物丧志。上蔡汗流浃背。面发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恻隐之心。且道上蔡闻过惭惶。自是羞恶之心。如何却说恻隐。是有恻隐之心方会动。动了始有羞恶。有恭敬。有是非。动处便是恻隐。若不会动。却不成人。天
之心。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物便是天之心。○问。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曰。且只得就恻隐字上看。○问。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且以恻隐论之。本只是这恻隐。遇当辞让则为辞让。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让。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个春气。发生之初为春气。发生得过。便为夏。收敛便为秋。消缩尽便为冬。明年又从春起。浑然只是一个发生之气。○问。仁包四者。然恻隐之端。如何贯得是非羞恶辞让之类。曰。恻隐只是动处。接事物时。皆是此心先拥出来。其间却自有羞恶是非之别。所以恻隐又贯四德。如春和则发生。夏则长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气。只是这个生意。○问。仁兼四端意。曰。上蔡见明道先生举史书成诵。明道谓其玩物丧志。上蔡汗流浃背。面发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恻隐之心。且道上蔡闻过惭惶。自是羞恶之心。如何却说恻隐。是有恻隐之心方会动。动了始有羞恶。有恭敬。有是非。动处便是恻隐。若不会动。却不成人。天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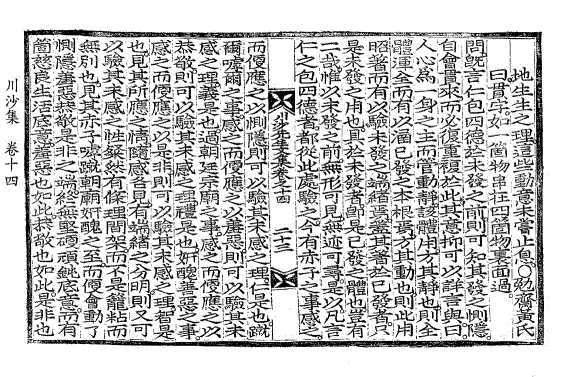 地生生之理。这些动意未尝止息。○勉斋黄氏曰。贯字。如一个物串在四个物里面过。
地生生之理。这些动意未尝止息。○勉斋黄氏曰。贯字。如一个物串在四个物里面过。问。既言仁包四德于未发之前。则可知其发之恻隐。自会贯来。而必复重复于此。其意抑可以详言与。曰。人心为一身之主而管动静。该体用。方其静也。则全体浑全而有以涵已发之本根焉。方其动也。则此用昭著而有以验未发之端绪焉。盖其著于已发者。只是未发之用也。具于未发者。即是已发之体也。岂有二哉。惟以未发之前。无形可见。无迹可寻。是以。凡言仁之包四德者。都从此处验之。今有赤子之事感之。而便应之以恻隐。则可以验其未感之理。仁是也。蹴尔嘑尔之事。感之而便应之以羞恶。则可以验其未感之理。义是也。过朝廷宗庙之事。感之而便应之以恭敬。则可以验其未感之理。礼是也。妍丑善恶之事。感之而便应之以是非。则可以验其未感之理。智是也。见其所应之情。随感各见。有端绪之分明。则又可以验其未感之性粲然有条理间架。而不是笼粘而无别也。见其赤子嘑蹴朝庙妍丑之至。而便会动了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端。终无坚硬顽钝底意。而有个慈良生活底意。羞恶也如此。恭敬也如此。是非也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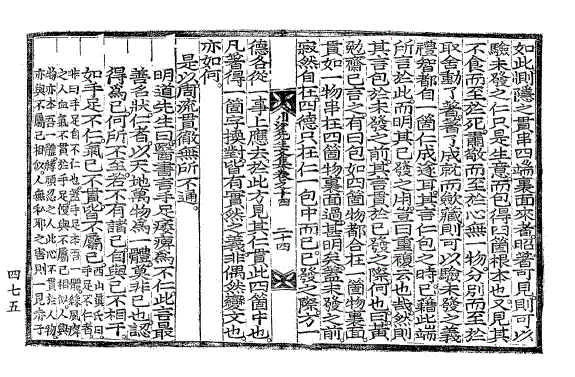 如此。恻隐之贯串四端里面来者。昭著可见。则可以验未发之仁只是生意。而包得四个根本也。又见其不食而至于死。肃敬而至于心无一物。分别而至于取舍动了著。著了成就而敛藏。则可以验未发之义礼智都自一个仁成遂耳。其言仁包之时。已藉此端所言于此。而明其已发之用。岂曰重复云也哉。然则其言包于未发之前。其言贯于已发之际。何也。曰。黄勉斋已言之。有曰包如四个物都合在一个物里面。贯如一物串在四个物里面过。甚明矣。盖未发之前。寂然自在。四德只在仁一包中而已。已发之际。方一德各从一事上应去。于此方见其仁贯此四个中也。凡著得一个字换对。皆有实然之义。非偶然变文也。亦如何。
如此。恻隐之贯串四端里面来者。昭著可见。则可以验未发之仁只是生意。而包得四个根本也。又见其不食而至于死。肃敬而至于心无一物。分别而至于取舍动了著。著了成就而敛藏。则可以验未发之义礼智都自一个仁成遂耳。其言仁包之时。已藉此端所言于此。而明其已发之用。岂曰重复云也哉。然则其言包于未发之前。其言贯于已发之际。何也。曰。黄勉斋已言之。有曰包如四个物都合在一个物里面。贯如一物串在四个物里面过。甚明矣。盖未发之前。寂然自在。四德只在仁一包中而已。已发之际。方一德各从一事上应去。于此方见其仁贯此四个中也。凡著得一个字换对。皆有实然之义。非偶然变文也。亦如何。是以。周流贯彻。无所不通。
明道先生曰。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西山真氏曰。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盖手足本吾一体。缘风痹之人血气不贯于手足。便与不属己相似。人与物亦本吾一体。缘顽忍之人此心不贯于人物。亦与不属己相似。人无私邪之害则一见赤子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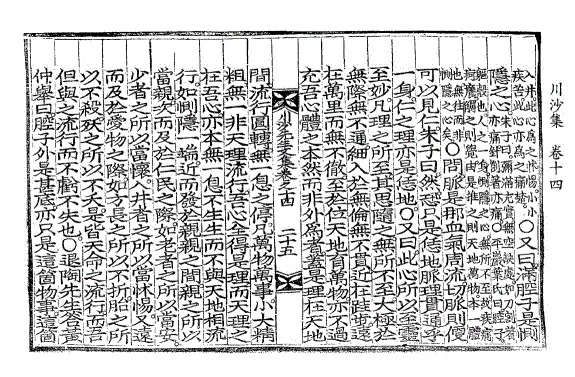 入井。此心为之怵惕。小小疾苦。此心亦为之痛楚。)○又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朱子曰。弥满充实。无空缺处。如刀割着亦痛。针劄著亦痛。○平岩叶氏曰。腔子。躯壳也。人之一身。恻隐之心。无所不至。故疾痛疴痒。触之则觉。由是推之则天地万物。本一体也。无往而非恻隐之心矣。)○问。脉是那血气周流。切脉则便可以见仁。朱子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贯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曰。此心所以至灵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随之。无所不至。大极于无际无不通。细入于无伦无不贯。近在跬步。远在万里而无不彻。至于位天地育万物。亦不过充吾心体之本然而非外为者。盖是理在天地间。流行圆转。无一息之停。凡万物万事。小大精粗。无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无一息不生生而不与天地相流行。如恻隐一端。近而发于亲亲之间。亲之所以当亲。次而及于仁民之际。如老者之所以当安。少者之所以当怀。入井者之所以当怵惕。又远而及于爱物之际。如方长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杀。夭之所以不夭。是皆天命之流行。而吾但与之流行而不亏不失也。○退陶先生答黄仲举曰。腔子外是甚底。亦只是这个物事。这个
入井。此心为之怵惕。小小疾苦。此心亦为之痛楚。)○又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朱子曰。弥满充实。无空缺处。如刀割着亦痛。针劄著亦痛。○平岩叶氏曰。腔子。躯壳也。人之一身。恻隐之心。无所不至。故疾痛疴痒。触之则觉。由是推之则天地万物。本一体也。无往而非恻隐之心矣。)○问。脉是那血气周流。切脉则便可以见仁。朱子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贯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曰。此心所以至灵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随之。无所不至。大极于无际无不通。细入于无伦无不贯。近在跬步。远在万里而无不彻。至于位天地育万物。亦不过充吾心体之本然而非外为者。盖是理在天地间。流行圆转。无一息之停。凡万物万事。小大精粗。无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无一息不生生而不与天地相流行。如恻隐一端。近而发于亲亲之间。亲之所以当亲。次而及于仁民之际。如老者之所以当安。少者之所以当怀。入井者之所以当怵惕。又远而及于爱物之际。如方长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杀。夭之所以不夭。是皆天命之流行。而吾但与之流行而不亏不失也。○退陶先生答黄仲举曰。腔子外是甚底。亦只是这个物事。这个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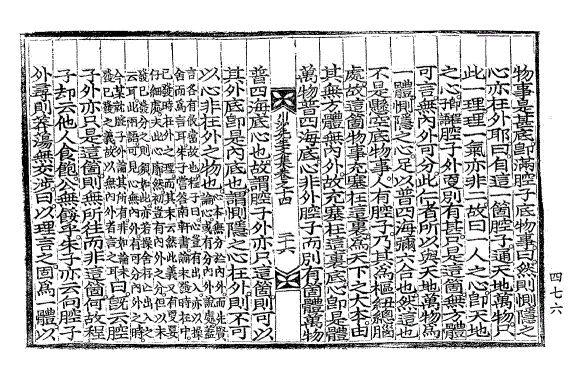 物事是甚底。即满腔子底物事。曰。然则恻隐之心亦在外耶。曰。自这一个腔子。通天地万物。只此一理。理一气亦非二。故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即程子语)腔子外更别有甚。只是这个。无方体可言。无内外可分。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然这也不是悬空底物事。人有腔子。乃其为枢纽总脑处。故这个物事充塞在这里。为天下之大本。由其无方体无内外。故充塞在这里底。心即是体万物普四海底。心非外腔子而别有个体万物普四海底心也。故谓腔子外亦只这个。则可以其外底即是内底也。谓恻隐之心在外。则不可以心非在外之物也。(心本无分于内外。而先贤论心。或有分内外说处。盖言各有攸当故也。程子曰。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为言耳。朱子尝答南轩书。论未发时在中。已发时在外之理。而其末云然此义又有更要仔细处。夫此心廓然。初岂有内外之分。但以未发已发分之则须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此两语。可见心无内外。有可分内外之时。今某就腔子外论其所有。非如论未发已发之义。故以无内外者言之耳。)曰。既云腔子外亦只是这个。则无所往而非这个。何故程子却云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朱子亦云向腔子外寻则莽荡无交涉。曰。以理言之。固为一体。以
物事是甚底。即满腔子底物事。曰。然则恻隐之心亦在外耶。曰。自这一个腔子。通天地万物。只此一理。理一气亦非二。故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即程子语)腔子外更别有甚。只是这个。无方体可言。无内外可分。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足以普四海弥六合也。然这也不是悬空底物事。人有腔子。乃其为枢纽总脑处。故这个物事充塞在这里。为天下之大本。由其无方体无内外。故充塞在这里底。心即是体万物普四海底。心非外腔子而别有个体万物普四海底心也。故谓腔子外亦只这个。则可以其外底即是内底也。谓恻隐之心在外。则不可以心非在外之物也。(心本无分于内外。而先贤论心。或有分内外说处。盖言各有攸当故也。程子曰。心岂有出入。亦以操舍而为言耳。朱子尝答南轩书。论未发时在中。已发时在外之理。而其末云然此义又有更要仔细处。夫此心廓然。初岂有内外之分。但以未发已发分之则须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此两语。可见心无内外。有可分内外之时。今某就腔子外论其所有。非如论未发已发之义。故以无内外者言之耳。)曰。既云腔子外亦只是这个。则无所往而非这个。何故程子却云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朱子亦云向腔子外寻则莽荡无交涉。曰。以理言之。固为一体。以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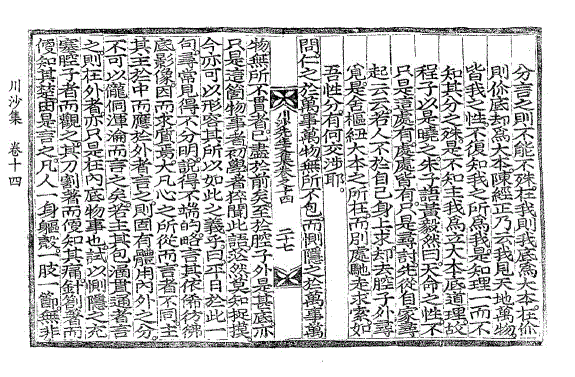 分言之则不能不殊。在我则我底为大本。在你则你底却为大本。陈经正乃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之所为我。是知理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是不知主我为立大本底道理。故程子以是晓之。朱子语黄毅然曰。天命之性。不只是这处有。处处皆有。只是寻讨。先从自家寻起云云。若人不于自己身上求。却去腔子外寻觅。是舍枢纽大本之所在。而别处驰走求索。如吾性分。有何交涉耶。
分言之则不能不殊。在我则我底为大本。在你则你底却为大本。陈经正乃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之所为我。是知理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是不知主我为立大本底道理。故程子以是晓之。朱子语黄毅然曰。天命之性。不只是这处有。处处皆有。只是寻讨。先从自家寻起云云。若人不于自己身上求。却去腔子外寻觅。是舍枢纽大本之所在。而别处驰走求索。如吾性分。有何交涉耶。问。仁之于万事万物。无所不包。而恻隐之于万事万物。无所不贯者。已尽于前矣。至于腔子外是甚底。亦只是这个物事者。初学者猝闻此语。茫然莫知捉摸。今亦可以形容其所以如此之义乎。曰。平日于此一句。寻常见得不分明。说得不端的。略言其依俙彷佛底影像。因而求质焉。大凡心之所从而言者不同。主其主于中而应于外者言之。则固有体用内外之分。不可以儱侗浑沦而言之矣。若主其包涵贯通者言之。则在外者。亦只是在内底物事也。试以恻隐之充塞腔子者而观之。其刀割著而便知其痛。针劄著而便知其楚。由是言之。凡人一身躯壳。一肢一节。无非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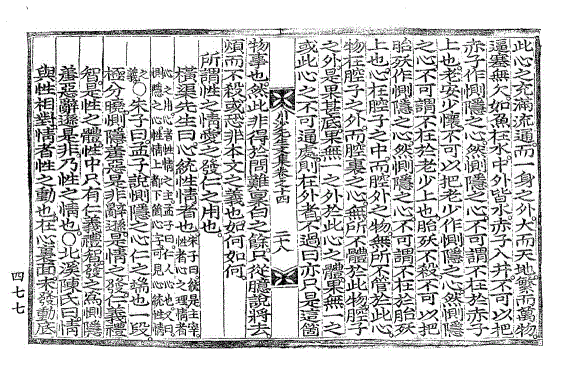 此心之充满流通。而一身之外。大而天地。繁而万物。逼塞无欠。如鱼在水。中外皆水。赤子入井。不可以把赤子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赤子上也。老安少怀。不可以把老少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老少上也。胎夭不杀。不可以把胎夭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胎夭上也。心在腔子之中。而腔外之物。无所不管于此心。物在腔子之外。而腔里之心。无所不体于此物。腔子之外。是果甚底。果无一之外于此心之体。果无一之或此心之不可通处。则在外者。不过曰亦只是这个物事也。然此非得于问难禀白之馀。只从臆说将去。烦而不杀。或恐非本文之义也。如何如何。
此心之充满流通。而一身之外。大而天地。繁而万物。逼塞无欠。如鱼在水。中外皆水。赤子入井。不可以把赤子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赤子上也。老安少怀。不可以把老少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老少上也。胎夭不杀。不可以把胎夭作恻隐之心。然恻隐之心。不可谓不在于胎夭上也。心在腔子之中。而腔外之物。无所不管于此心。物在腔子之外。而腔里之心。无所不体于此物。腔子之外。是果甚底。果无一之外于此心之体。果无一之或此心之不可通处。则在外者。不过曰亦只是这个物事也。然此非得于问难禀白之馀。只从臆说将去。烦而不杀。或恐非本文之义也。如何如何。所谓性之情。爱之发。仁之用也。
横渠先生曰。心统性情者也。(朱子曰。统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恻隐之心。性情上都下个心字。可见心统性情之义。)○朱子曰。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段。极分晓。恻隐羞恶是非辞逊。是情之发。仁义礼智。是性之体。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发之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乃性之情也。○北溪陈氏曰。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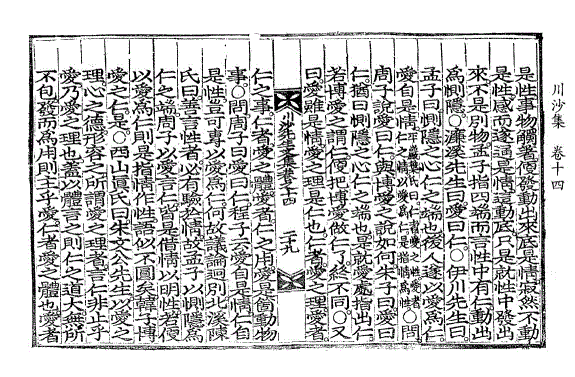 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底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孟子指四端而言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隐。○濂溪先生曰。爱曰仁。○伊川先生曰。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后人遂以爱为仁。爱自是情。(平岩叶氏曰。仁者爱之性。爱者仁之情。以爱为仁。是指情为性。)○问。周子说爱曰仁。与博爱之说如何。朱子曰。爱曰仁。犹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就爱处指出仁。若博爱之谓仁。便把博爱做仁了。终不同。○又曰。爱虽是情。爱之理是仁也。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爱是个动物事。○问。周子曰爱曰仁。程子云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何故议论迥别。北溪陈氏曰。善言性者。必有验于情。故孟子以恻隐为仁之端。周子以爱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爱为仁则是指情作性。语似不圆矣。韩子博爱之仁。是。○西山真氏曰。朱文公先生。以爱之理。心之德。形容之。所谓爱之理者。言仁非止乎爱。乃爱之理也。盖以体言之则仁之道大。无所不包。发而为用则主乎爱。仁者爱之体也。爱者
是性。事物触著。便发动出来底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孟子指四端而言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隐。○濂溪先生曰。爱曰仁。○伊川先生曰。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后人遂以爱为仁。爱自是情。(平岩叶氏曰。仁者爱之性。爱者仁之情。以爱为仁。是指情为性。)○问。周子说爱曰仁。与博爱之说如何。朱子曰。爱曰仁。犹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是就爱处指出仁。若博爱之谓仁。便把博爱做仁了。终不同。○又曰。爱虽是情。爱之理是仁也。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爱是个动物事。○问。周子曰爱曰仁。程子云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何故议论迥别。北溪陈氏曰。善言性者。必有验于情。故孟子以恻隐为仁之端。周子以爱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爱为仁则是指情作性。语似不圆矣。韩子博爱之仁。是。○西山真氏曰。朱文公先生。以爱之理。心之德。形容之。所谓爱之理者。言仁非止乎爱。乃爱之理也。盖以体言之则仁之道大。无所不包。发而为用则主乎爱。仁者爱之体也。爱者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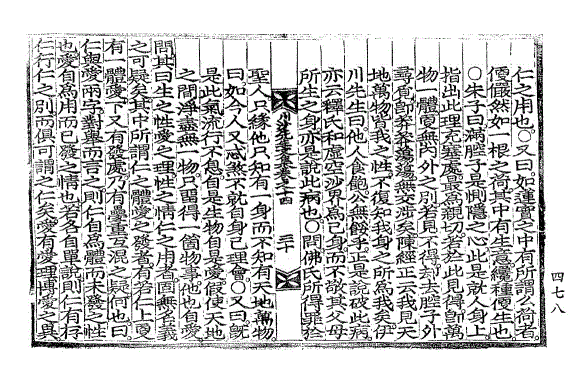 仁之用也。○又曰。如莲实之中有所谓幺荷者。便俨然如一根之荷。其中有生意。才种便生也。○朱子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若于此见得。即万物一体。更无内外之别。若见不得。却去腔子外寻觅。即莽莽荡荡。无交涉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所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亦云释氏和虚空沙界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说此病也。○问。佛氏所得罪于圣人。只缘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万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会。○又曰。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尽无一物。只留得一个物事。他也自爱。
仁之用也。○又曰。如莲实之中有所谓幺荷者。便俨然如一根之荷。其中有生意。才种便生也。○朱子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若于此见得。即万物一体。更无内外之别。若见不得。却去腔子外寻觅。即莽莽荡荡。无交涉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所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亦云释氏和虚空沙界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说此病也。○问。佛氏所得罪于圣人。只缘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万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己理会。○又曰。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尽无一物。只留得一个物事。他也自爱。问。其曰生之性爱之理。性之情仁之用者。固无名义之可疑矣。其中所谓仁之体爱之发者。有若仁上更有一体爱。下又有发处。乃有叠重互混之疑。何也。曰。仁与爱两字。对举而言之。则仁自为体而未发之性也。爱自为用而已发之情也。若各自单说。则仁有存仁行仁之别。而俱可谓之仁矣。爱有爱理博爱之异。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9H 页
 而并可谓之爱矣。仁之体云者。因用而指体也。爱之发云者。据性而言情也。初不必致疑于斯也。(答。此段看得恐未然。所谓生之性爱之理者。以专偏言仁之体。故以仁之体也四字结之。所谓性之情爱之发者。以专偏言仁之用。故以仁之用也四字结之。初非据性而言情。因用而指体也。)且既分体用性情。两下齐头。仁字时已知为爱之体也。爱字时已知为仁之发也。而爱之一字。不足以尽仁道之全体。仁之发处。只是曰爱而已。则若曰爱之体则失仁体之浑全矣。又曰仁之发。则太宽而似不贴里。其曰仁之体爱之发者。不亦完全而衬切矣乎。曰。仁说既分体用而言。则今观附录。先儒之语。或未免有参涉侵犯。不分界破处。或一语重见于上下。只分详略而附之。其亦不为含糊之甚与。曰。果有然矣。有论性情而一句之中。俱兼两义则或并录于前。有一句兼两义而意趣有归。则从其意趣而附之。如无所不统。无所不通。主在于天地同体。如爱之理爱之发。主在于近著身己。而先儒之言。论此甚多。而或一篇之中。首主乎彼而末主乎此。始发于此而终与于彼。则或断截而分其类。或重叠而开其旨。而抑有一处可疑。谨按朱子与南轩
而并可谓之爱矣。仁之体云者。因用而指体也。爱之发云者。据性而言情也。初不必致疑于斯也。(答。此段看得恐未然。所谓生之性爱之理者。以专偏言仁之体。故以仁之体也四字结之。所谓性之情爱之发者。以专偏言仁之用。故以仁之用也四字结之。初非据性而言情。因用而指体也。)且既分体用性情。两下齐头。仁字时已知为爱之体也。爱字时已知为仁之发也。而爱之一字。不足以尽仁道之全体。仁之发处。只是曰爱而已。则若曰爱之体则失仁体之浑全矣。又曰仁之发。则太宽而似不贴里。其曰仁之体爱之发者。不亦完全而衬切矣乎。曰。仁说既分体用而言。则今观附录。先儒之语。或未免有参涉侵犯。不分界破处。或一语重见于上下。只分详略而附之。其亦不为含糊之甚与。曰。果有然矣。有论性情而一句之中。俱兼两义则或并录于前。有一句兼两义而意趣有归。则从其意趣而附之。如无所不统。无所不通。主在于天地同体。如爱之理爱之发。主在于近著身己。而先儒之言。论此甚多。而或一篇之中。首主乎彼而末主乎此。始发于此而终与于彼。则或断截而分其类。或重叠而开其旨。而抑有一处可疑。谨按朱子与南轩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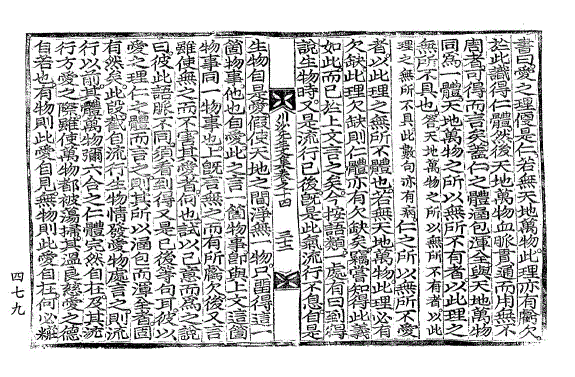 书曰。爱之理便是仁。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于此识得仁体。然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用无不周者。可得而言矣。盖仁之体涵包浑全。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天地万物之所以无所不有者。以此理之无所不具也。(答。天地万物之所以无所不有者。以此理之无所不具。此数句亦有病。)仁之所以无所不爱者。以此理之无所不体也。若无天地万物。此理必有欠缺。此理欠缺则仁体亦有欠缺矣。窃尝知得此义如此。而已于上文言之矣。今按语类。一处有曰到得说生物时。又是流行已后。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无一物。只留得这一个物事。他也自爱。此之言一个物事。即与上文这个物事同一物事也。上既言无之而有所亏欠。后又言虽使无之而不害其爱者。何也。试以己意而为之说曰。彼此语脉不同。须看到得又是已后等句耳。彼以爱之理仁之体而言之。则其所以涵包而浑全者。固有然矣。此段。截自流行生物情发爱物处言之。则流行以前。其体万物弥六合之仁体完然自在。及其流行方爱之际。虽使万物都被荡扫。其温良慈爱之德自若也。有物则此爱自见。无物则此爱自在。何必妆
书曰。爱之理便是仁。若无天地万物。此理亦有亏欠。于此识得仁体。然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用无不周者。可得而言矣。盖仁之体涵包浑全。与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天地万物之所以无所不有者。以此理之无所不具也。(答。天地万物之所以无所不有者。以此理之无所不具。此数句亦有病。)仁之所以无所不爱者。以此理之无所不体也。若无天地万物。此理必有欠缺。此理欠缺则仁体亦有欠缺矣。窃尝知得此义如此。而已于上文言之矣。今按语类。一处有曰到得说生物时。又是流行已后。既是此气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爱。假使天地之间净无一物。只留得这一个物事。他也自爱。此之言一个物事。即与上文这个物事同一物事也。上既言无之而有所亏欠。后又言虽使无之而不害其爱者。何也。试以己意而为之说曰。彼此语脉不同。须看到得又是已后等句耳。彼以爱之理仁之体而言之。则其所以涵包而浑全者。固有然矣。此段。截自流行生物情发爱物处言之。则流行以前。其体万物弥六合之仁体完然自在。及其流行方爱之际。虽使万物都被荡扫。其温良慈爱之德自若也。有物则此爱自见。无物则此爱自在。何必妆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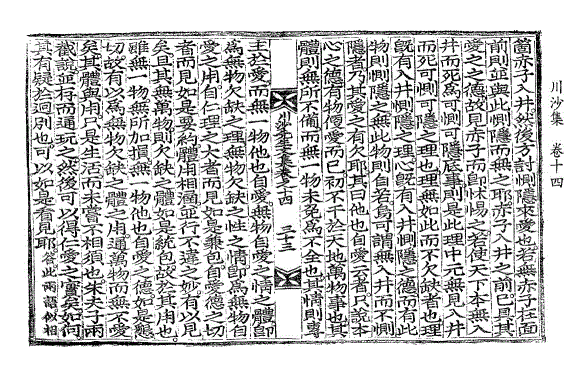 个赤子入井。然后方讨恻隐来爱也。若无赤子在面前则并与此恻隐而无之耶。赤子入井之前。已具其爱之之德。故见赤子而即怵惕之。若使天下本无入井而死为可恻可隐底事。则是此理中元无见入井而死可恻可隐之理也。理无如此而不欠缺者也。理既有入井恻隐之理。心既有入井恻隐之德。而有此物则恻隐之。无此物则自若。乌可谓无入井而不恻隐者。乃其爱之有欠耶。其曰他也自爱云者。只说本心之德。有物便爱而已。初不干于天地万物事也。其体则无所不备。而无一物未免为不全也。其情则专主于爱。而无一物他也自爱。无物自爱之情之体。即为无物欠缺之理。无物欠缺之性之情。即为无物自爱之用。自仁理之大者而见如是兼包。自爱德之切者而见如是要约。体用相涵。并行不违之妙。有以见矣。且其无万物。则欠缺之体如是统包。故于其用也。虽无一物。无所加损。无一物他也自爱之德。如是恳切。故有以为无物欠缺之体之用。通万物而无不爱矣。其体与用。只是生活。而未尝不相须也。朱夫子两截说。并存而通玩之。然后可以得仁爱之实矣。如何。其有疑于迥别也。可以如是看见耶。(答。此两语。似相
个赤子入井。然后方讨恻隐来爱也。若无赤子在面前则并与此恻隐而无之耶。赤子入井之前。已具其爱之之德。故见赤子而即怵惕之。若使天下本无入井而死为可恻可隐底事。则是此理中元无见入井而死可恻可隐之理也。理无如此而不欠缺者也。理既有入井恻隐之理。心既有入井恻隐之德。而有此物则恻隐之。无此物则自若。乌可谓无入井而不恻隐者。乃其爱之有欠耶。其曰他也自爱云者。只说本心之德。有物便爱而已。初不干于天地万物事也。其体则无所不备。而无一物未免为不全也。其情则专主于爱。而无一物他也自爱。无物自爱之情之体。即为无物欠缺之理。无物欠缺之性之情。即为无物自爱之用。自仁理之大者而见如是兼包。自爱德之切者而见如是要约。体用相涵。并行不违之妙。有以见矣。且其无万物。则欠缺之体如是统包。故于其用也。虽无一物。无所加损。无一物他也自爱之德。如是恳切。故有以为无物欠缺之体之用。通万物而无不爱矣。其体与用。只是生活。而未尝不相须也。朱夫子两截说。并存而通玩之。然后可以得仁爱之实矣。如何。其有疑于迥别也。可以如是看见耶。(答。此两语。似相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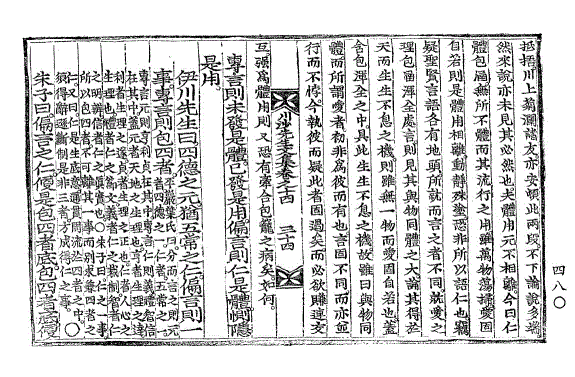 抵捂。川上菊澜诸友。亦安顿此两段。不下论说多端。然来说亦未见其必然也。夫体用元不相离。今曰仁体包涵。无所不体而其流行之用。虽万物荡扫。爱固自若则是体用相离。动静殊涂。恐非所以语仁也。窃疑圣贤言语各有地头。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就爱之理包涵浑全处言。则见其与物同体之大。论其得于天而生生不息之机。则虽无一物而爱固自若也。盖含包浑全之中。具此生生不息之机。故虽曰与物同体。而所谓爱者。初非为彼而有也。言固不同。而亦并行而不悖。今执彼而疑此者固过矣。而必欲赚连交互。强为体用则又恐有牵合包笼之病矣。如何。)
抵捂。川上菊澜诸友。亦安顿此两段。不下论说多端。然来说亦未见其必然也。夫体用元不相离。今曰仁体包涵。无所不体而其流行之用。虽万物荡扫。爱固自若则是体用相离。动静殊涂。恐非所以语仁也。窃疑圣贤言语各有地头。所就而言之者不同。就爱之理包涵浑全处言。则见其与物同体之大。论其得于天而生生不息之机。则虽无一物而爱固自若也。盖含包浑全之中。具此生生不息之机。故虽曰与物同体。而所谓爱者。初非为彼而有也。言固不同。而亦并行而不悖。今执彼而疑此者固过矣。而必欲赚连交互。强为体用则又恐有牵合包笼之病矣。如何。)专言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偏言则仁是体。恻隐是用。
伊川先生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平岩叶氏曰。分而言之则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专言元则亨利贞在其中。专言仁则义礼智信在其中。盖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达。利者生理之遂。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实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离其一事而别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须得辞逊断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朱子曰。偏言之仁。便是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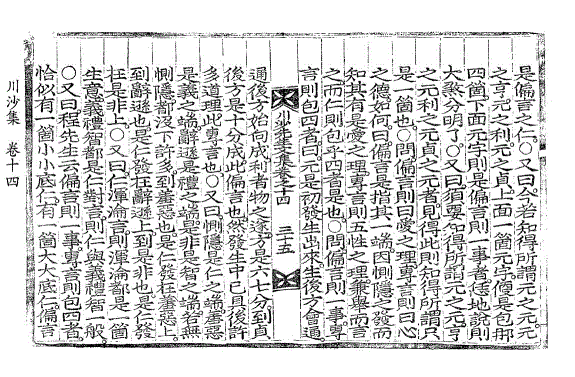 是偏言之仁。○又曰。今若知得所谓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上面一个元字。便是包那四个。下面元字则是偏言则一事者。恁地说则大煞分明了。○又曰。须要知得所谓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者。见得此则知得所谓只是一个也。○问。偏言则曰爱之理。专言则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恻隐之发而知其有是爱之理。专言则五性之理。兼举而言之。而仁则包乎四者是也。○问。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后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又曰。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又曰。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又曰。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
是偏言之仁。○又曰。今若知得所谓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上面一个元字。便是包那四个。下面元字则是偏言则一事者。恁地说则大煞分明了。○又曰。须要知得所谓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者。见得此则知得所谓只是一个也。○问。偏言则曰爱之理。专言则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恻隐之发而知其有是爱之理。专言则五性之理。兼举而言之。而仁则包乎四者是也。○问。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后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又曰。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又曰。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又曰。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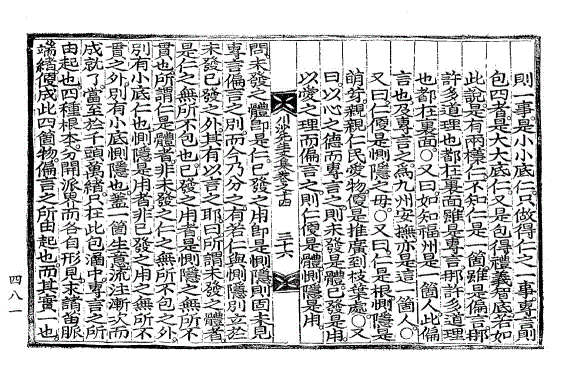 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又曰。如知福州是一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又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又曰。以心之德而专言之。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以爱之理而偏言之。则仁便是体。恻隐是用。
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又曰。如知福州是一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又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又曰。以心之德而专言之。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以爱之理而偏言之。则仁便是体。恻隐是用。问。未发之体即是仁。已发之用即是恻隐。则固未见专言偏言之别。而今乃分之。有若仁与恻隐别立于未发已发之外。其有以言之耶。曰。所谓未发之体者。是仁之无所不包也。已发之用者。是恻隐之无所不贯也。所谓仁是体者。非未发之仁之无所不包之外。别有小底仁也。恻隐是用者。非已发之用之无所不贯之外。别有小底恻隐也。盖一个生意。流注渐次而成就了。当至于千头万绪。只在此包涵中。专言之所由起也。四种根本。分开派界而各自形见。求诸苗脉端绪。便成此四个物。偏言之所由起也。而其实一也。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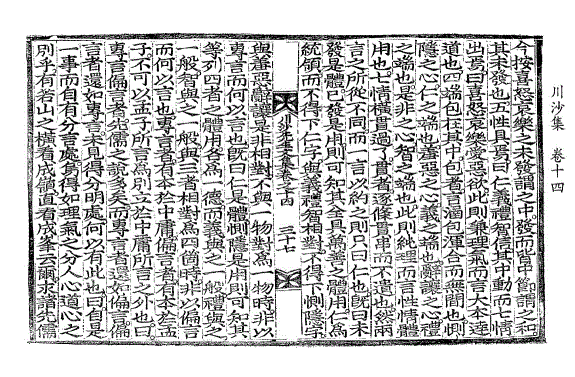 今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此则兼理气而言大本达道也。四端包在其中。包者。言涵包浑合而无间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则纯理而言性情体用也。七情横贯过了。贯者。逐条贯串而不遗也。然两言之所从不同。而一言以约之则只曰仁也。既曰未发是体。已发是用。则可知其全具万善之体用。仁为统领。而不得下仁字。与义礼智相对。不得下恻隐字。与羞恶辞让是非相对。不与一物对为一物时。非以专言而何以言也。既曰仁是体。恻隐是用则可知其等列四者之体用。各为一德。而义与之一般。礼与之一般。智与之一般。与三者相对为四个时。非以偏言而何以言也。专言者。有本于中庸。偏言者。有本于孟子。不可以孟子所言为别立于中庸所言之外也。曰。专言偏言者。先儒之说多矣。而专言者还如偏言。偏言者还如专言。未见得分明处。何以有此也。曰。自是一事而自有分言处。乌得如理气之分人心道心之别乎。有若山之横看成岭。直看成峰云尔。求诸先儒
今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乐爱恶欲。此则兼理气而言大本达道也。四端包在其中。包者。言涵包浑合而无间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则纯理而言性情体用也。七情横贯过了。贯者。逐条贯串而不遗也。然两言之所从不同。而一言以约之则只曰仁也。既曰未发是体。已发是用。则可知其全具万善之体用。仁为统领。而不得下仁字。与义礼智相对。不得下恻隐字。与羞恶辞让是非相对。不与一物对为一物时。非以专言而何以言也。既曰仁是体。恻隐是用则可知其等列四者之体用。各为一德。而义与之一般。礼与之一般。智与之一般。与三者相对为四个时。非以偏言而何以言也。专言者。有本于中庸。偏言者。有本于孟子。不可以孟子所言为别立于中庸所言之外也。曰。专言偏言者。先儒之说多矣。而专言者还如偏言。偏言者还如专言。未见得分明处。何以有此也。曰。自是一事而自有分言处。乌得如理气之分人心道心之别乎。有若山之横看成岭。直看成峰云尔。求诸先儒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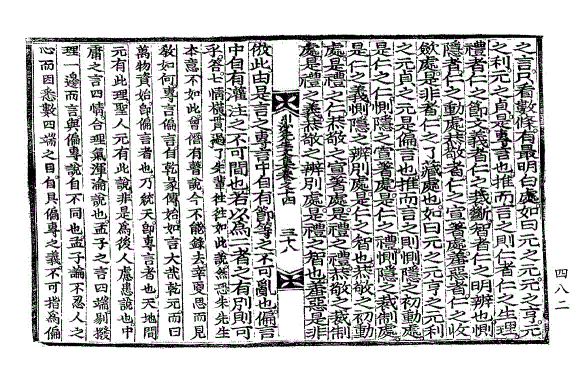 之言。只看数条。有最明白处。如曰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是专言也。推而言之则仁者仁之生理。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裁断。智者仁之明辨也。恻隐者。仁之动处。恭敬者。仁之宣著处。羞恶者。仁之收敛处。是非者。仁之了藏处也。如曰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是偏言也。推而言之则恻隐之初动处。是仁之仁。恻隐之宣著处。是仁之礼。恻隐之裁制处。是仁之义。恻隐之辨别处。是仁之智也。恭敬之初动处。是礼之仁。恭敬之宣著处。是礼之礼。恭敬之裁制处。是礼之义。恭敬之辨别处。是礼之智也。羞恶是非仿此。由是言之。专言中自有节等之不可乱也。偏言中自有灌注之不可间也。若以为二者之有别则可乎。(答。七情横贯过了。先辈往往如此说。然恐朱先生本意不如此。曾僭有瞽说。今不能录去。幸更思而见教如何。专言偏言。自乾彖传始。如言大哉乾元。而曰万物资始。即偏言者也。乃统天。即专言者也。天地间元有此理。圣人元有此说。非是为后人虑患说也。中庸之言四情。合理气浑沦说也。孟子之言四端。剔拨理一边而言。与偏专说自不同也。孟子论不忍人之心而因悉数四端之目。自具偏专之义。不可指为偏
之言。只看数条。有最明白处。如曰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是专言也。推而言之则仁者仁之生理。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裁断。智者仁之明辨也。恻隐者。仁之动处。恭敬者。仁之宣著处。羞恶者。仁之收敛处。是非者。仁之了藏处也。如曰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是偏言也。推而言之则恻隐之初动处。是仁之仁。恻隐之宣著处。是仁之礼。恻隐之裁制处。是仁之义。恻隐之辨别处。是仁之智也。恭敬之初动处。是礼之仁。恭敬之宣著处。是礼之礼。恭敬之裁制处。是礼之义。恭敬之辨别处。是礼之智也。羞恶是非仿此。由是言之。专言中自有节等之不可乱也。偏言中自有灌注之不可间也。若以为二者之有别则可乎。(答。七情横贯过了。先辈往往如此说。然恐朱先生本意不如此。曾僭有瞽说。今不能录去。幸更思而见教如何。专言偏言。自乾彖传始。如言大哉乾元。而曰万物资始。即偏言者也。乃统天。即专言者也。天地间元有此理。圣人元有此说。非是为后人虑患说也。中庸之言四情。合理气浑沦说也。孟子之言四端。剔拨理一边而言。与偏专说自不同也。孟子论不忍人之心而因悉数四端之目。自具偏专之义。不可指为偏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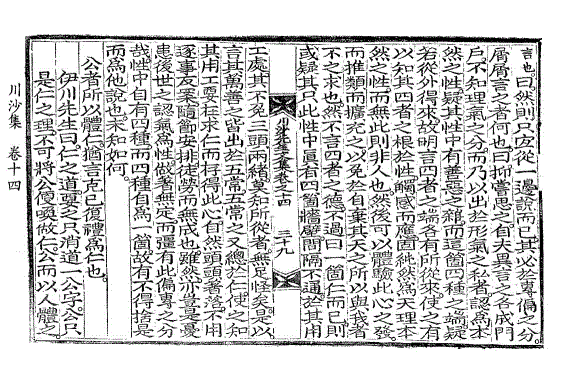 言也。)曰。然则只宜从一边说而已。其必于专偏之分。屑屑言之者何也。曰。抑尝思之。自夫异言之各成门户。不知理气之分。而乃以出于形气之私者。认为本然之性。疑其性中有善恶之杂。而这个四种之端。疑若从外得来。故明言四者之端各有所从来。使之有以知其四者之根于性。触感而应。固纯然为天理本然之性。而无此则非人也。然后可以体验此心之发。而推类而扩充之。以免于自弃其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之求也。然不言四者之德。不过曰一个仁而已。则或疑其只此性中真有四个墙壁。间隔不通。于其用工处。其不免三头两绪。莫知所从者。无足怪矣。是以。言其万善之皆出于五常。五常之又总于仁。使之知其用工要在求仁而存得此心。自然头头著落。不用逐事反案。随节安排。徒劳而无成也。虽然。亦岂是忧患后世之认气为性。做著无定。而彊有此偏专之分哉。性中自有四种。而四种自为一个。故有不得舍是而为他说也。未知如何。
言也。)曰。然则只宜从一边说而已。其必于专偏之分。屑屑言之者何也。曰。抑尝思之。自夫异言之各成门户。不知理气之分。而乃以出于形气之私者。认为本然之性。疑其性中有善恶之杂。而这个四种之端。疑若从外得来。故明言四者之端各有所从来。使之有以知其四者之根于性。触感而应。固纯然为天理本然之性。而无此则非人也。然后可以体验此心之发。而推类而扩充之。以免于自弃其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之求也。然不言四者之德。不过曰一个仁而已。则或疑其只此性中真有四个墙壁。间隔不通。于其用工处。其不免三头两绪。莫知所从者。无足怪矣。是以。言其万善之皆出于五常。五常之又总于仁。使之知其用工要在求仁而存得此心。自然头头著落。不用逐事反案。随节安排。徒劳而无成也。虽然。亦岂是忧患后世之认气为性。做著无定。而彊有此偏专之分哉。性中自有四种。而四种自为一个。故有不得舍是而为他说也。未知如何。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也。
伊川先生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公而以人体之。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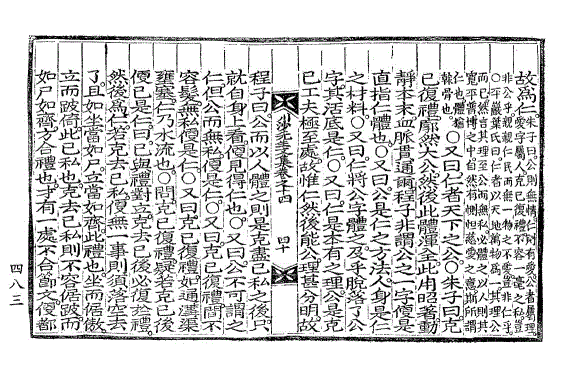 故为仁。(朱子曰。公则无情。仁则有爱。公者属理。爱字属人。克己复礼。不容一毫之私。岂非公乎。亲亲仁民而无一物之不爱。岂非仁乎。○平岩叶氏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无私。必体之以人则其宽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恻怛慈爱之意。斯所谓仁也。体犹干骨也。)○又曰。仁者天下之公。○朱子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尔。程子非谓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体也。○又曰。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又曰。仁将公字体之。及乎脱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又曰。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又曰。克己复礼。如通沟渠壅塞。仁乃水流也。○问。克己复礼。疑若克己后便已是仁。曰。己与礼对立。克去己后必复于礼。然后为仁。若克去己私。便无一事则须落空去了。且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此礼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则不容倨跛。而如尸如齐。方合礼也。才有一处不合节文。便都
故为仁。(朱子曰。公则无情。仁则有爱。公者属理。爱字属人。克己复礼。不容一毫之私。岂非公乎。亲亲仁民而无一物之不爱。岂非仁乎。○平岩叶氏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无私。必体之以人则其宽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恻怛慈爱之意。斯所谓仁也。体犹干骨也。)○又曰。仁者天下之公。○朱子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动静本末。血脉贯通尔。程子非谓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体也。○又曰。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又曰。仁将公字体之。及乎脱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极至处。故惟仁然后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则是克尽己私之后。只就自身上看。便见得仁也。○又曰。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又曰。克己复礼。如通沟渠壅塞。仁乃水流也。○问。克己复礼。疑若克己后便已是仁。曰。己与礼对立。克去己后必复于礼。然后为仁。若克去己私。便无一事则须落空去了。且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此礼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则不容倨跛。而如尸如齐。方合礼也。才有一处不合节文。便都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4H 页
 是私意。佛氏之学。超出世故。无足以累其心。不可谓之有私意。然只见他空底。不见实理。所以都无规矩准绳。便尽是私意。○问。克己复礼即仁乎。曰。克己复礼。当下便是仁。非复礼之外别有仁也。此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问。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尽得公道。所以为仁耳。求仁处。圣人说了克己复礼为仁。须是克尽己私。以复乎礼。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又曰。程子云惟公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才公。仁便在此故云近。○又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盖公犹无尘。人犹镜也。仁则犹镜之光明也。○又曰。仁是人心固有之理。未可便以公为仁。须是体之以人。方是仁。○问。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窃谓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万事。本是吾身至亲至切处。公只是仁之理。专言公则只虚空说著理。而不见其切于己。故必以身体之。然后我与理合而谓之仁。犹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体。如之何而谓之仁。亦不过克尽己私。至于此心豁然。莹净光洁。洞彻表里。纯是天理之公。生生无间断则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
是私意。佛氏之学。超出世故。无足以累其心。不可谓之有私意。然只见他空底。不见实理。所以都无规矩准绳。便尽是私意。○问。克己复礼即仁乎。曰。克己复礼。当下便是仁。非复礼之外别有仁也。此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问。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尽得公道。所以为仁耳。求仁处。圣人说了克己复礼为仁。须是克尽己私。以复乎礼。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又曰。程子云惟公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才公。仁便在此故云近。○又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盖公犹无尘。人犹镜也。仁则犹镜之光明也。○又曰。仁是人心固有之理。未可便以公为仁。须是体之以人。方是仁。○问。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窃谓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万事。本是吾身至亲至切处。公只是仁之理。专言公则只虚空说著理。而不见其切于己。故必以身体之。然后我与理合而谓之仁。犹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体。如之何而谓之仁。亦不过克尽己私。至于此心豁然。莹净光洁。洞彻表里。纯是天理之公。生生无间断则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4L 页
 寂而未发。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于地中之复。无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随感而动也。恻然有隐。如阳春发达于地上。无一物一事非此生理之贯。此体公之所以为仁。所以能恕能爱。或为义为礼为智为信。无所往而不通也。不审是否。曰。此说得之。
寂而未发。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于地中之复。无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随感而动也。恻然有隐。如阳春发达于地上。无一物一事非此生理之贯。此体公之所以为仁。所以能恕能爱。或为义为礼为智为信。无所往而不通也。不审是否。曰。此说得之。问。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所以明公之非直指仁体而以人体之故仁也。又以公字贴了克己复礼以后。而以公之体仁。贴了克复之为仁也。可以详言之与。曰。由其私意净尽。只是纯然天理而谓之公也。由其私意净尽。纯然天理之中。有慈爱恻怛之意。而为人心德者而谓之仁也。不可将那私意净尽。纯然天理底。作这慈爱恻怛底看也。是公之不可谓仁。而到此私意已尽。纯然天理了。体此公在人身上则斯有恻怛慈爱本心之德。而动静本末。血脉贯通。正如克得己私尽。复得天理尽了。此体浑全而此用昭著也。然则公非仁而公而体之。仁也。克复非仁而克复了生意流通。仁也。不亦互相发明耶。前此只将公字。作只是祛了私己狭小底看。而不带理字看。故疑其克己了方公。公后方复礼。复礼是仁也。是以。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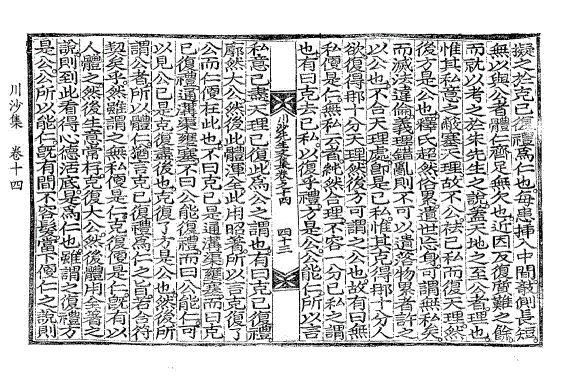 拟之于克己复礼为仁也。每患插入中间。攲侧长短。无以与公者体仁齐足无欠也。近因反复质难之馀。而就以考之于朱先生之说。盖天地之至公者。理也。惟其私意之蔽塞天理。故不公。祛己私而复天理。然后方是公也。释氏超然俗累。遗世忘身。可谓无私矣。而灭法违伦。义理错乱则不可以遗落物累者许之以公也。不合天理处。即是己私。惟其克得那十分人欲。复得那十分天理。然后方可谓之公也。故有曰无私便是仁。无私云者。纯然合理。不容一分己私之谓也。有曰克去己私。以复乎礼。方是公。公能仁。所以言私意已尽。天理已复。此为公之谓也。有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所以言克复了公而仁便在此也。不曰克己是通沟渠壅塞。而曰克己复礼。通沟渠壅塞。不曰公能复礼。而曰公能仁。可以见公已是克复尽后也。克复了方是公也。然后所谓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之旨。若合符契矣乎。然虽谓之无私便是仁。克复便是仁。既有以人体之。然后生意常存。克复大公。然后体用全著之说。则到此看得心德活底。是为仁也。虽谓之复礼方是公。公所以能仁。既有间不容发。当下便仁之说则
拟之于克己复礼为仁也。每患插入中间。攲侧长短。无以与公者体仁齐足无欠也。近因反复质难之馀。而就以考之于朱先生之说。盖天地之至公者。理也。惟其私意之蔽塞天理。故不公。祛己私而复天理。然后方是公也。释氏超然俗累。遗世忘身。可谓无私矣。而灭法违伦。义理错乱则不可以遗落物累者许之以公也。不合天理处。即是己私。惟其克得那十分人欲。复得那十分天理。然后方可谓之公也。故有曰无私便是仁。无私云者。纯然合理。不容一分己私之谓也。有曰克去己私。以复乎礼。方是公。公能仁。所以言私意已尽。天理已复。此为公之谓也。有曰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然后此体浑全。此用昭著。所以言克复了公而仁便在此也。不曰克己是通沟渠壅塞。而曰克己复礼。通沟渠壅塞。不曰公能复礼。而曰公能仁。可以见公已是克复尽后也。克复了方是公也。然后所谓公者。所以体仁。犹言克己复礼为仁之旨。若合符契矣乎。然虽谓之无私便是仁。克复便是仁。既有以人体之。然后生意常存。克复大公。然后体用全著之说。则到此看得心德活底。是为仁也。虽谓之复礼方是公。公所以能仁。既有间不容发。当下便仁之说则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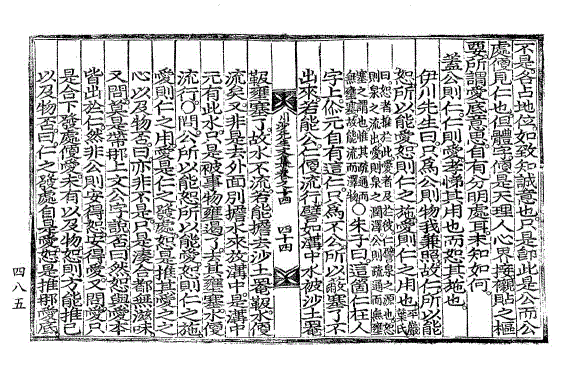 不是。各占地位。如致知诚意也。只是即此是公而公处便见仁也。但体字。便是天理人心界接。衬贴之枢要。所谓爱底意思。自有分明处耳。未知如何。
不是。各占地位。如致知诚意也。只是即此是公而公处便见仁也。但体字。便是天理人心界接。衬贴之枢要。所谓爱底意思。自有分明处耳。未知如何。盖公则仁。仁则爱。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
伊川先生曰。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平岩叶氏曰。恕者推于此。爱者及于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则泉之流出。爱则泉之润泽。公则疏通而无壅塞之谓也。惟其疏通而无壅塞。故能流而泽物。)○朱子曰。这个仁在人字上。你元自有这仁。只为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来。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沟中水被沙土罨靸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担去沙土罨靸。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别担水来放沟中。是沟中元有此水。只是被事物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问。公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爱是仁之发处。恕是推其爱之之心以及物否。曰。亦非不是。只是凑合都无滋味。又问。莫是带那上文公字说否。曰然。恕与爱本皆出于仁。然非公则安得恕。安得爱。又问。爱只是合下发处便爱。未有以及物。恕则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发处自是爱。恕是推那爱底。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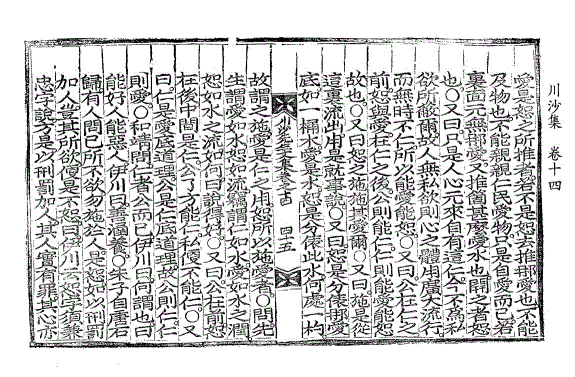 爱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爱也。不能及物也。不能亲亲仁民爱物。只是自爱而已。若里面元无那爱。又推个甚么爱水也。开之者恕也。○又曰。只是人心元来自有这仁。今不为私欲所蔽尔。故人无私欲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而无时不仁。所以能爱能恕。○又曰。公在仁之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仁则能爱能恕故也。○又曰恕之施施其爱尔○又曰。施是从这里流出。用是就事说。○又曰。恕是分俵那爱底。如一桶水。爱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处一杓。故谓之施。爱是仁之用。恕所以施爱者。○问。先生谓爱如水。恕如流。窃谓仁如水。爱如水之润。恕如水之流。如何。曰说得好。○又曰。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又曰。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和靖问。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朱子自唐石归。有人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如以刑罚加人。岂其所欲。便是不恕。曰。伊川云恕字须兼忠字说。方是。以刑罚加人。其人实有罪。其心亦
爱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爱也。不能及物也。不能亲亲仁民爱物。只是自爱而已。若里面元无那爱。又推个甚么爱水也。开之者恕也。○又曰。只是人心元来自有这仁。今不为私欲所蔽尔。故人无私欲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而无时不仁。所以能爱能恕。○又曰。公在仁之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仁则能爱能恕故也。○又曰恕之施施其爱尔○又曰。施是从这里流出。用是就事说。○又曰。恕是分俵那爱底。如一桶水。爱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处一杓。故谓之施。爱是仁之用。恕所以施爱者。○问。先生谓爱如水。恕如流。窃谓仁如水。爱如水之润。恕如水之流。如何。曰说得好。○又曰。公在前。恕在后。中间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又曰。仁是爱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则仁。仁则爱。○和靖问。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朱子自唐石归。有人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如以刑罚加人。岂其所欲。便是不恕。曰。伊川云恕字须兼忠字说。方是。以刑罚加人。其人实有罪。其心亦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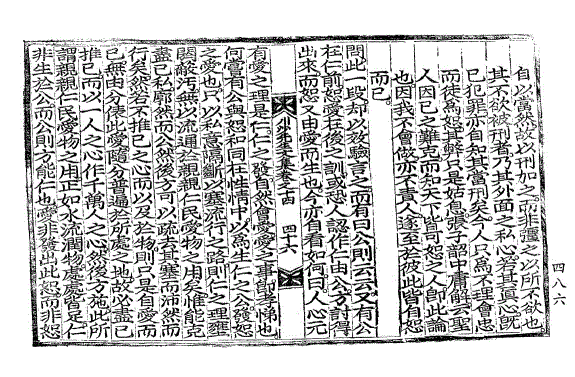 自以当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彊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当刑矣。今人只为不理会忠而徒为恕。其弊只是姑息。张子韶中庸解。云圣人因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论也。因我不会做。亦不责人。遂至于彼此皆自恕而已。
自以当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彊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当刑矣。今人只为不理会忠而徒为恕。其弊只是姑息。张子韶中庸解。云圣人因己之难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论也。因我不会做。亦不责人。遂至于彼此皆自恕而已。问。此一段。却以效验言之。而有曰公则云云。又有公在仁前。恕爱在后之训。或恐人认作仁由公。方讨得出来。而恕又由爱而生也。今亦自看如何。曰。人心元有爱之理是仁。仁之发。自然会爱。爱之事。即孝悌也。何尝有公与恕和同在性情中。以为生仁之公。发恕之爱也。只以私意隔断。以塞流行之路。则仁之理壅阏蔽污。无以流通于亲亲仁民爱物之用矣。惟能克尽己私。廓然而公。然后方可以疏去其塞而沛然而行矣。然若不推己之心而以及于物。则只是自爱而已。无由分俵此爱。随分普遍于所处之地。故必尽己推己。而以一人之心作千万人之心。然后方施。此所谓亲亲仁民爱物之用。正如水流润物。处处皆足。仁非生于公。而公则方能仁也。爱非发出此恕。而非恕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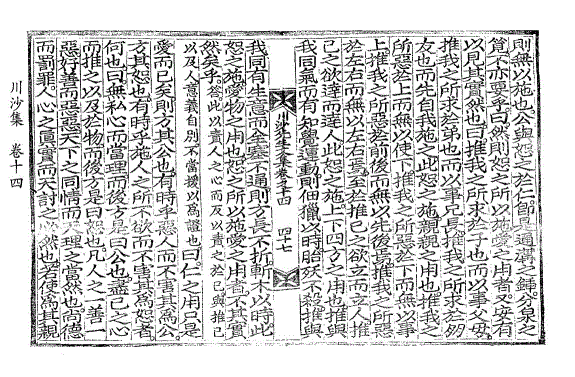 则无以施也。公与恕之于仁。即是通沟之锸。分泉之笕。不亦要乎。曰。然则恕之所以施爱之用者。又安有以见其实然也。曰。推我之所求于子也而以事父母。推我之所求于弟也而以事兄长。推我之所求于朋友也而先自我施之。此恕之施。亲亲之用也。推我之所恶于上而无以使下。推我之所恶于下而无以事上。推我之所恶于前后而无以先后焉。推我之所恶于左右而无以左右焉。至于推己之欲立而立人。推己之欲达而达人。此恕之施。上下四方之用也。推与我同气而有知觉运动。则佃猎以时。胎夭不杀。推与我同有生意而全塞不通。则方长不折。斩木以时。此恕之施。爱物之用也。恕之所以施爱之用者。不其实然矣乎。(答。此以责人之心而反以责之于己。与推己以及人。意义自别。不当援以为證也。)曰。仁之用只是爱而已矣。则方其公也。有时乎恶人而不害其为公。方其恕也。有时乎施人之所不欲而不害其为恕者。何也。曰。无私心而当理。而后方是曰公也。尽己之心而推之以及于物。而后方是曰恕也。凡人之一善一恶。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而天理之当然也。尚德而罚罪。人心之真实而天讨之必然也。若使为其亲
则无以施也。公与恕之于仁。即是通沟之锸。分泉之笕。不亦要乎。曰。然则恕之所以施爱之用者。又安有以见其实然也。曰。推我之所求于子也而以事父母。推我之所求于弟也而以事兄长。推我之所求于朋友也而先自我施之。此恕之施。亲亲之用也。推我之所恶于上而无以使下。推我之所恶于下而无以事上。推我之所恶于前后而无以先后焉。推我之所恶于左右而无以左右焉。至于推己之欲立而立人。推己之欲达而达人。此恕之施。上下四方之用也。推与我同气而有知觉运动。则佃猎以时。胎夭不杀。推与我同有生意而全塞不通。则方长不折。斩木以时。此恕之施。爱物之用也。恕之所以施爱之用者。不其实然矣乎。(答。此以责人之心而反以责之于己。与推己以及人。意义自别。不当援以为證也。)曰。仁之用只是爱而已矣。则方其公也。有时乎恶人而不害其为公。方其恕也。有时乎施人之所不欲而不害其为恕者。何也。曰。无私心而当理。而后方是曰公也。尽己之心而推之以及于物。而后方是曰恕也。凡人之一善一恶。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而天理之当然也。尚德而罚罪。人心之真实而天讨之必然也。若使为其亲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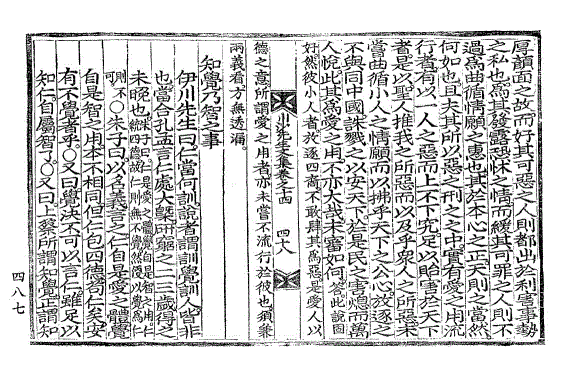 厚颜面之故。而好其可恶之人则都出于利害事势之私也。为其发露恐怵之情。而缓其可罪之人则不过为曲循情愿之惠也。其于本心之正。天则之当然。何如也。且夫其所以恶之刑之之中。实有爱之用流行者。有以一人之恶而上不下究。足以贻害于天下者。是以。圣人推我之所恶而以及乎众人之所恶。未尝曲循小人之情愿而以拂乎天下之公心。放逐之不与同中国。诛戮之以安天下。于是民之害熄而万人悦。此其为爱之用。不亦大哉。未审如何。(答。此说固好。然彼小人者。放逐四裔。不敢肆其为恶。是爱人以德之意。所谓爱之用者。亦未尝不流行于彼也。须兼两义看。方无透漏。)
厚颜面之故。而好其可恶之人则都出于利害事势之私也。为其发露恐怵之情。而缓其可罪之人则不过为曲循情愿之惠也。其于本心之正。天则之当然。何如也。且夫其所以恶之刑之之中。实有爱之用流行者。有以一人之恶而上不下究。足以贻害于天下者。是以。圣人推我之所恶而以及乎众人之所恶。未尝曲循小人之情愿而以拂乎天下之公心。放逐之不与同中国。诛戮之以安天下。于是民之害熄而万人悦。此其为爱之用。不亦大哉。未审如何。(答。此说固好。然彼小人者。放逐四裔。不敢肆其为恶。是爱人以德之意。所谓爱之用者。亦未尝不流行于彼也。须兼两义看。方无透漏。)知觉乃智之事
伊川先生曰。仁当何训。说者谓训觉训人。皆非也。当合孔孟言仁处大槩。研穷之二三岁得之未晚也。(朱子曰。仁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仁统四德。故仁则无不觉。然便以觉为仁则不可。)○朱子曰。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觉者乎。○又曰。觉决不可以言仁。虽足以知仁。自属智了。○又曰。上蔡所谓知觉。正谓知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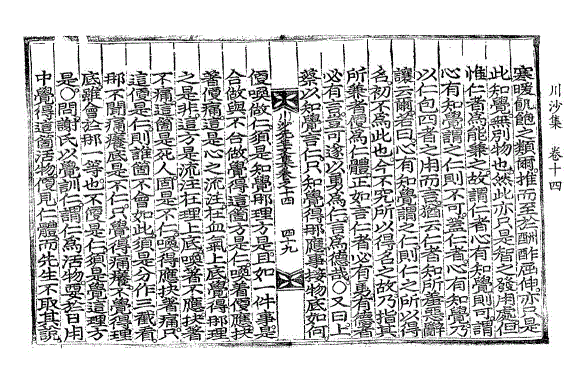 寒暖饥饱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屈伸。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盖仁者。心有知觉。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犹云仁者知所羞恶辞让云尔。若曰。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仁之所以得名。初不为此也。今不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岂可遂以勇为仁。言为德哉。○又曰。上蔡以知觉言仁。只知觉得那应事接物底如何。便唤做仁。须是知觉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与不合做。觉得这个方是仁。唤着便应。抉著便痛。这是心之流注。在血气上底。觉得那理之是非。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唤著不应。抉著不痛。这个是死人。固是不仁。唤得应抉著痛。只这便是仁。则谁个不会如此。须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闻痛痒底是不仁。只觉得痛痒。不觉得理底。虽会于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须是觉这理方是。○问。谢氏以觉训仁。谓仁为活物。要于日用中觉得这个活物。便见仁体。而先生不取其说。
寒暖饥饱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屈伸。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盖仁者。心有知觉。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犹云仁者知所羞恶辞让云尔。若曰。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仁之所以得名。初不为此也。今不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岂可遂以勇为仁。言为德哉。○又曰。上蔡以知觉言仁。只知觉得那应事接物底如何。便唤做仁。须是知觉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与不合做。觉得这个方是仁。唤着便应。抉著便痛。这是心之流注。在血气上底。觉得那理之是非。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唤著不应。抉著不痛。这个是死人。固是不仁。唤得应抉著痛。只这便是仁。则谁个不会如此。须是分作三截看。那不闻痛痒底是不仁。只觉得痛痒。不觉得理底。虽会于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须是觉这理方是。○问。谢氏以觉训仁。谓仁为活物。要于日用中觉得这个活物。便见仁体。而先生不取其说。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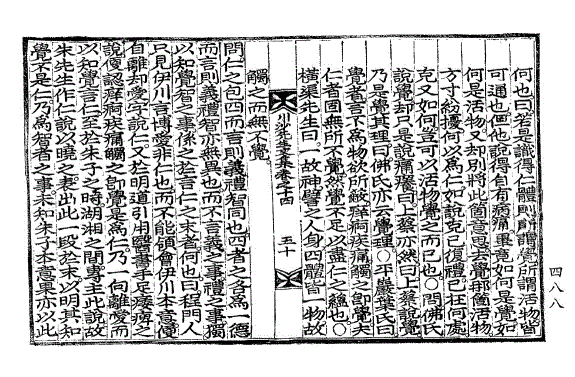 何也。曰。若是识得仁体则所谓觉。所谓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说得自有病痛。毕竟如何是觉。如何是活物。又却别将此个意思。去觉那个活物。方寸纷扰。何以为仁。如说克己复礼。己在何处。克又如何。岂可以活物觉之而已也。○问。佛氏说觉。却只是说痛痒。曰。上蔡亦然。曰。上蔡说觉。乃是觉其理。曰。佛氏亦云觉理。○平岩叶氏曰。觉者。言不为物欲所蔽。痒痾疾痛。触之即觉。夫仁者固无所不觉。然觉不足以尽仁之蕴也。○横渠先生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触之而无不觉。
何也。曰。若是识得仁体则所谓觉。所谓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说得自有病痛。毕竟如何是觉。如何是活物。又却别将此个意思。去觉那个活物。方寸纷扰。何以为仁。如说克己复礼。己在何处。克又如何。岂可以活物觉之而已也。○问。佛氏说觉。却只是说痛痒。曰。上蔡亦然。曰。上蔡说觉。乃是觉其理。曰。佛氏亦云觉理。○平岩叶氏曰。觉者。言不为物欲所蔽。痒痾疾痛。触之即觉。夫仁者固无所不觉。然觉不足以尽仁之蕴也。○横渠先生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触之而无不觉。问。仁之包四而言则义礼智同也。四者之各为一德而言则义礼智亦无异也。而不言义之事。礼之事。独以知觉智之事。系之于言仁之末者。何也。曰。程门人只见伊川言博爱非仁也。而不能领会伊川本意。便自离却爱字说仁。又于明道引用医书手足痿痹之说。便认痒痾疾痛触之即觉是为仁。乃一向离爱而以知觉言仁。至于朱子之时。湖湘之间。专主此说。故朱先生作仁说以晓之。表出此一段于末。以明其知觉不是仁。乃为智者之事。未知朱子本意果亦以此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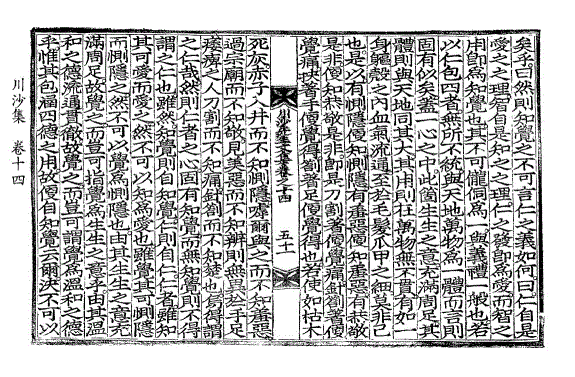 矣乎。曰然则知觉之不可言仁之义如何。曰。仁自是爱之之理。智自是知之之理。仁之发即为爱。而智之用即为知觉也。其不可儱侗为一。与义礼一般也。若以仁包四者。无所不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言则固有似矣。盖一心之中。此个生生之意。充满周足。其体则与天地同其大。其用则在万物无不贯。有如一身躯壳之内血气流通。至于毛发爪甲之细。莫非己也。是以。有恻隐便知恻隐。有羞恶便知羞恶。有恭敬是非。便知恭敬是非。即是刀割著便觉痛。针劄著便觉痛。抉著手便觉得。劄著足便觉得也。若使如枯木死灰。赤子入井而不知恻隐。嘑尔与之而不知羞恶。过宗庙而不知敬。见美恶而不知辨则无异于手足痿痹之人刀割而不知痛。针劄而不知楚也。乌得谓之仁哉。然则仁者之心。固有知觉。而无知觉则不得谓之仁也。虽然。知觉则自知觉。仁则自仁。仁者。虽知其可爱而爱之。然不可以知为爱也。虽觉其可恻隐而恻隐之。然不可以觉为恻隐也。由其生生之意充满周足。故觉之。而岂可指觉为生生之意乎。由其温和之德流通贯彻。故觉之。而岂可谓觉为温和之德乎。惟其包涵四德之用。故便自知觉云尔。决不可以
矣乎。曰然则知觉之不可言仁之义如何。曰。仁自是爱之之理。智自是知之之理。仁之发即为爱。而智之用即为知觉也。其不可儱侗为一。与义礼一般也。若以仁包四者。无所不统。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言则固有似矣。盖一心之中。此个生生之意。充满周足。其体则与天地同其大。其用则在万物无不贯。有如一身躯壳之内血气流通。至于毛发爪甲之细。莫非己也。是以。有恻隐便知恻隐。有羞恶便知羞恶。有恭敬是非。便知恭敬是非。即是刀割著便觉痛。针劄著便觉痛。抉著手便觉得。劄著足便觉得也。若使如枯木死灰。赤子入井而不知恻隐。嘑尔与之而不知羞恶。过宗庙而不知敬。见美恶而不知辨则无异于手足痿痹之人刀割而不知痛。针劄而不知楚也。乌得谓之仁哉。然则仁者之心。固有知觉。而无知觉则不得谓之仁也。虽然。知觉则自知觉。仁则自仁。仁者。虽知其可爱而爱之。然不可以知为爱也。虽觉其可恻隐而恻隐之。然不可以觉为恻隐也。由其生生之意充满周足。故觉之。而岂可指觉为生生之意乎。由其温和之德流通贯彻。故觉之。而岂可谓觉为温和之德乎。惟其包涵四德之用。故便自知觉云尔。决不可以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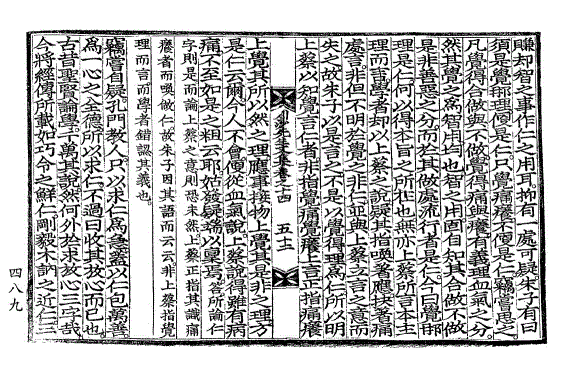 赚却智之事作仁之用耳。抑有一处可疑。朱子有曰须是觉那理。便是仁。只觉痛痒。不便是仁。窃尝思之。凡觉得合做与不做。觉得痛与痒。有义理血气之分。然其觉之为智用。均也。智之用。固自知其合做不做是非善恶之分。而于其做处流行者是仁。今曰觉那理是仁。何以得本旨之所在也。无亦上蔡所言本主理而言。学者却以上蔡之说。疑其指唤著应。抉著痛处言。非但不明于觉之非仁。并与上蔡立言之意而失之。故朱子以是言之。不是以觉得理为仁。所以明上蔡以知觉言仁者。非指觉痛觉痒上言。正指痛痒上觉其所以然之理。应事接物上觉其是非之理。方是仁云尔。今人不会。便从血气说。上蔡说得虽有病痛。不至如是之粗云耶。姑发疑端以禀焉。(答。所论仁字则是。而论上蔡之意则恐未然。上蔡正指其识痛痒者而唤做仁。故朱子因其语而云云。非上蔡指觉理而言。而学者错认其义也。)
赚却智之事作仁之用耳。抑有一处可疑。朱子有曰须是觉那理。便是仁。只觉痛痒。不便是仁。窃尝思之。凡觉得合做与不做。觉得痛与痒。有义理血气之分。然其觉之为智用。均也。智之用。固自知其合做不做是非善恶之分。而于其做处流行者是仁。今曰觉那理是仁。何以得本旨之所在也。无亦上蔡所言本主理而言。学者却以上蔡之说。疑其指唤著应。抉著痛处言。非但不明于觉之非仁。并与上蔡立言之意而失之。故朱子以是言之。不是以觉得理为仁。所以明上蔡以知觉言仁者。非指觉痛觉痒上言。正指痛痒上觉其所以然之理。应事接物上觉其是非之理。方是仁云尔。今人不会。便从血气说。上蔡说得虽有病痛。不至如是之粗云耶。姑发疑端以禀焉。(答。所论仁字则是。而论上蔡之意则恐未然。上蔡正指其识痛痒者而唤做仁。故朱子因其语而云云。非上蔡指觉理而言。而学者错认其义也。)窃尝自疑。孔门教人。只以求仁为急。盖以仁包万善。为一心之全德。所以求仁。不过曰收其放心而已也。古昔圣贤论学。千万其说。然何外于求放心三字哉。今将经传所载。如巧令之鲜仁。刚毅木讷之近仁。三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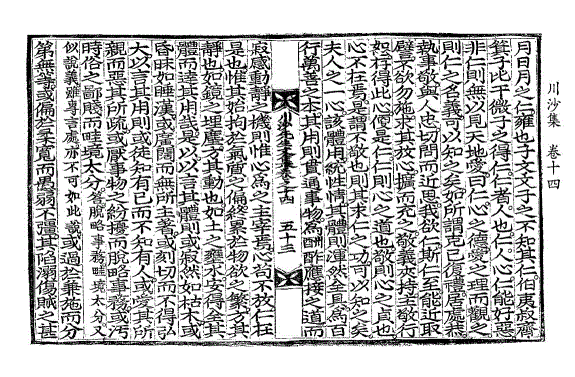 月日月之仁。雍也,子文,文子之不知其仁。伯夷,叔齐,箕子,比干,微子之得仁。仁者。人也。仁。人心。仁能好恶。非仁则无以见天地爱。曰仁。心之德。爱之理而观之。则仁之名义。可以知之矣。如所谓克己复礼。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切问而近思。我欲仁。斯仁至。能近取譬。不欲勿施。求其放心。扩而充之。敬义夹持。主敬行恕。存得此心。便是仁。仁则心之道也。敬则心之贞也。心不在焉。是谓不敬也则其求仁之功。可以知之矣。夫人之一心。该体用。统性情。其体则浑然全具。为百行万善之本。其用则贯通事物。为酬酢应接之道。而寂感动静之机则惟心为之主宰焉。心苟不放。仁在是也。惟其始拘于气质之偏。终累于物欲之繁。方其静也。如镜之埋尘。方其动也。如土之壅水。安得全其体而达其用哉。是以。以言其体则或寂然如枯木。或昏昧如睡汉。或广阔而无所主著。或刻切而不得弘大。以言其用则或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或爱其所亲而恶其所疏。或厌事物之纷扰而脱略事务。或污时俗之鄙贱而畦境太分。(答。脱略事务。畦境太分。又似说义。虽专言处。亦不可如此说。)或过于兼施而分第无等。或偏于柔宽而愚弱不彊。其陷溺伤贼之甚
月日月之仁。雍也,子文,文子之不知其仁。伯夷,叔齐,箕子,比干,微子之得仁。仁者。人也。仁。人心。仁能好恶。非仁则无以见天地爱。曰仁。心之德。爱之理而观之。则仁之名义。可以知之矣。如所谓克己复礼。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切问而近思。我欲仁。斯仁至。能近取譬。不欲勿施。求其放心。扩而充之。敬义夹持。主敬行恕。存得此心。便是仁。仁则心之道也。敬则心之贞也。心不在焉。是谓不敬也则其求仁之功。可以知之矣。夫人之一心。该体用。统性情。其体则浑然全具。为百行万善之本。其用则贯通事物。为酬酢应接之道。而寂感动静之机则惟心为之主宰焉。心苟不放。仁在是也。惟其始拘于气质之偏。终累于物欲之繁。方其静也。如镜之埋尘。方其动也。如土之壅水。安得全其体而达其用哉。是以。以言其体则或寂然如枯木。或昏昧如睡汉。或广阔而无所主著。或刻切而不得弘大。以言其用则或徒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或爱其所亲而恶其所疏。或厌事物之纷扰而脱略事务。或污时俗之鄙贱而畦境太分。(答。脱略事务。畦境太分。又似说义。虽专言处。亦不可如此说。)或过于兼施而分第无等。或偏于柔宽而愚弱不彊。其陷溺伤贼之甚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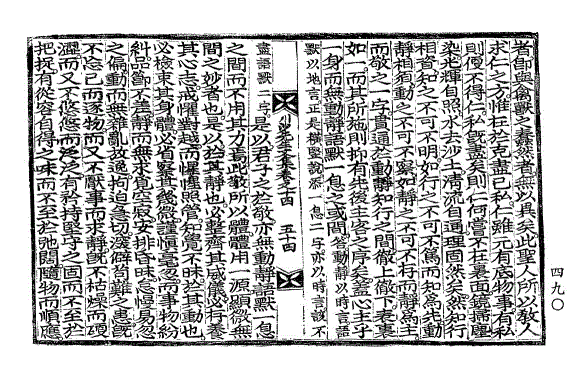 者。即与禽兽之蠢然者。无以异矣。此圣人所以教人求仁之方。惟在于克尽己私。仁虽元有底物事。有私则便不得仁。私既尽矣则仁何尝不在里面。镜扫尘染。光辉自照。水去沙土。清流自通。理固然矣。然知行相资。知之不可不明。如行之不可不笃而知为先。动静相须。动之不可不察。如静之不可不存而静为主。而敬之一字。贯通于动静知行之间。彻上彻下。表里如一。而其所施则抑有先后主客之序矣。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一息之或间。(答。动静以时言。语默以地言。正是横竖说。添一息二字。亦以时言。该不尽语默二字。)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一息之间而不用其力焉。此敬所以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妙者也。是以。于其静也。必整齐其威仪。必存养其心志。戒惧对越。而惺惺照管。知觉不昧。于其动也。必检束其身体。必省察其几微。谨慎毫忽。而事物纷纠。品节不差。静而无求觅空寂。安排昏昧。怠慢易忽之偏。动而无杂乱放逸。拘迫急切。深僻苟难之患。既不忘己而逐物。而又不厌事而求静。既不枯燥而硬涩。而又不悠悠而泛泛。有矜持坚守之固而不至于把捉。有从容自得之味而不至于弛阔。随物而顺应。
者。即与禽兽之蠢然者。无以异矣。此圣人所以教人求仁之方。惟在于克尽己私。仁虽元有底物事。有私则便不得仁。私既尽矣则仁何尝不在里面。镜扫尘染。光辉自照。水去沙土。清流自通。理固然矣。然知行相资。知之不可不明。如行之不可不笃而知为先。动静相须。动之不可不察。如静之不可不存而静为主。而敬之一字。贯通于动静知行之间。彻上彻下。表里如一。而其所施则抑有先后主客之序矣。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一息之或间。(答。动静以时言。语默以地言。正是横竖说。添一息二字。亦以时言。该不尽语默二字。)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一息之间而不用其力焉。此敬所以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妙者也。是以。于其静也。必整齐其威仪。必存养其心志。戒惧对越。而惺惺照管。知觉不昧。于其动也。必检束其身体。必省察其几微。谨慎毫忽。而事物纷纠。品节不差。静而无求觅空寂。安排昏昧。怠慢易忽之偏。动而无杂乱放逸。拘迫急切。深僻苟难之患。既不忘己而逐物。而又不厌事而求静。既不枯燥而硬涩。而又不悠悠而泛泛。有矜持坚守之固而不至于把捉。有从容自得之味而不至于弛阔。随物而顺应。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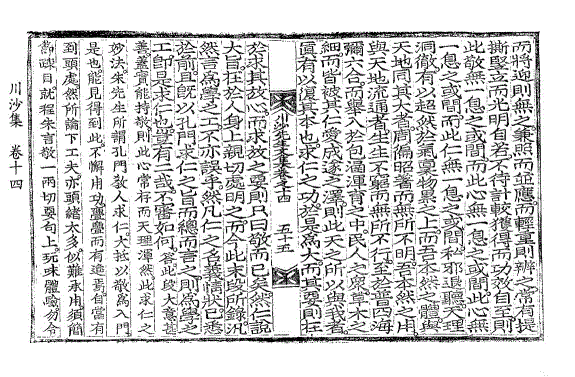 而将迎则无之。兼照而并应。而轻重则辨之。常有提撕竖立而光明自若。不待计较获得而功效自至。则此敬无一息之或间。而此心无一息之或间。此心无一息之或间。而此仁无一息之或间。私邪退听。天理洞彻。有以超然于气禀物累之上。而吾本然之体。与天地同其大者。周遍昭著而无所不明。吾本然之用。与天地流通者。生生不穷而无所不行。至于普四海弥六合。而举入于包涵浑育之中。民人之众。草木之细。而皆被其仁爱成遂之泽。则此天之所以与我者。真有以复其本也。求仁之功。于是为大。而其要则在于求其放心。而求放之要则只曰敬而已矣。然仁说大旨。在于人身上亲切处明之。而今此末段所录。汎然言为学之工。不亦误乎。然凡仁之名义情状。已悉于前。且既以孔门求仁之旨而总而言之。则为学之工。即是求仁也。岂有二哉。不审如何。(答。此段大意甚善。盖实能持敬。则此心常存而天理浑然。此求仁之妙法。朱先生所谓孔门教人求仁。大抵以敬为入门。是也。能见得到此。不懈用功。亹亹而有进焉。自当有到头处。然所论下工夫。亦头绪太多。似难承用。须简节疏目。就程朱言敬一两切要句上。玩味体验。勿令
而将迎则无之。兼照而并应。而轻重则辨之。常有提撕竖立而光明自若。不待计较获得而功效自至。则此敬无一息之或间。而此心无一息之或间。此心无一息之或间。而此仁无一息之或间。私邪退听。天理洞彻。有以超然于气禀物累之上。而吾本然之体。与天地同其大者。周遍昭著而无所不明。吾本然之用。与天地流通者。生生不穷而无所不行。至于普四海弥六合。而举入于包涵浑育之中。民人之众。草木之细。而皆被其仁爱成遂之泽。则此天之所以与我者。真有以复其本也。求仁之功。于是为大。而其要则在于求其放心。而求放之要则只曰敬而已矣。然仁说大旨。在于人身上亲切处明之。而今此末段所录。汎然言为学之工。不亦误乎。然凡仁之名义情状。已悉于前。且既以孔门求仁之旨而总而言之。则为学之工。即是求仁也。岂有二哉。不审如何。(答。此段大意甚善。盖实能持敬。则此心常存而天理浑然。此求仁之妙法。朱先生所谓孔门教人求仁。大抵以敬为入门。是也。能见得到此。不懈用功。亹亹而有进焉。自当有到头处。然所论下工夫。亦头绪太多。似难承用。须简节疏目。就程朱言敬一两切要句上。玩味体验。勿令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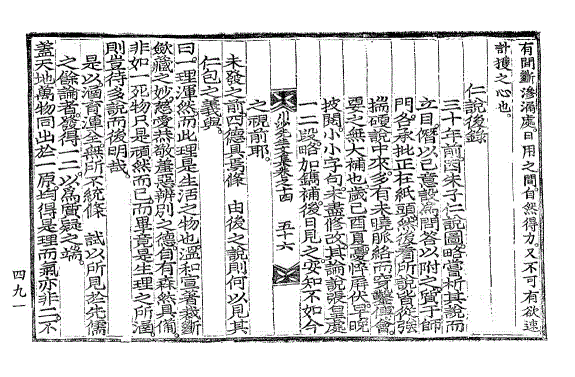 有间断渗漏处。日用之间。自然得力。又不可有欲速计获之心也。)
有间断渗漏处。日用之间。自然得力。又不可有欲速计获之心也。)仁说后录
三十年前。因朱子仁说图。略尝析其说而立目。僭以己意设为问答以附之。质于师门。各承批正在纸头。然后看所说皆从强揣硬说中来。多有未晓脉络而穿凿傅会。要之无大补也。岁己酉夏。忧悴屏伏。早晚披阅。小小字句。未尽修改。其论说张皇处一二段。略加镌补。后日见之。安知不如今之视前耶。
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条 由后之说则何以见其仁包之义与。
曰。一理浑然。而此理是生活之物也。温和宣著裁断敛藏之妙。慈爱恭敬羞恶辨别之德。自有森然具备。非如一死物只是顽然而已。而毕竟是生理之所涵。则岂待多说而后明哉。
是以。涵育浑全。无所不统条 试以所见于先儒之馀论者。发得一二。以为质疑之端。
盖天地万物同出于一原。均得是理而气亦非二。不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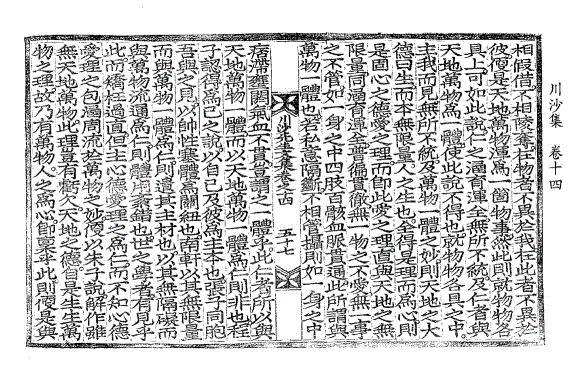 相假借。不相陵夺。在物者不异于我。在此者不异于彼。便是天地万物浑为一个物事。然此则就物物各具上。可如此说。仁之涵育浑全。无所不统。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此说不得也。就物物各具之中。主我而见。无所不统。及万物一体之妙。则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本无限量。人之生也。全得是理而为心。则是固心之德爱之理。而即此爱之理。直与天地之无限量。同涵育浑全。普遍贯彻。无一物之不爱。无一事之不管。如一身之中四肢百骸血脉贯通。此所谓与万物一体也。若私意隔断。不相管摄则如一身之中痞滞壅阏。气血不贯。岂谓之一体乎。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而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则非也。程子认得为己之说。以自己及彼为主本也。张子同胞吾与之见。以帅性塞体为关纽也。南轩以其无限量而与万物一体为仁。则遗其主材也。以其无隔碍而与万物流通为仁。则体用紊错也。世之学者。有见乎此。而矫枉过直。但主心德爱理之为仁。而不知心德爱理之包涵周流于万物之妙。便以朱子说。解作虽无天地万物。此理岂有亏欠。天地之德。自是生生万物之理。故乃有万物。人之为心。即禀乎此。则便是与
相假借。不相陵夺。在物者不异于我。在此者不异于彼。便是天地万物浑为一个物事。然此则就物物各具上。可如此说。仁之涵育浑全。无所不统。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此说不得也。就物物各具之中。主我而见。无所不统。及万物一体之妙。则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本无限量。人之生也。全得是理而为心。则是固心之德爱之理。而即此爱之理。直与天地之无限量。同涵育浑全。普遍贯彻。无一物之不爱。无一事之不管。如一身之中四肢百骸血脉贯通。此所谓与万物一体也。若私意隔断。不相管摄则如一身之中痞滞壅阏。气血不贯。岂谓之一体乎。此仁者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而以天地万物一体为仁则非也。程子认得为己之说。以自己及彼为主本也。张子同胞吾与之见。以帅性塞体为关纽也。南轩以其无限量而与万物一体为仁。则遗其主材也。以其无隔碍而与万物流通为仁。则体用紊错也。世之学者。有见乎此。而矫枉过直。但主心德爱理之为仁。而不知心德爱理之包涵周流于万物之妙。便以朱子说。解作虽无天地万物。此理岂有亏欠。天地之德。自是生生万物之理。故乃有万物。人之为心。即禀乎此。则便是与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2L 页
 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彼此内外也。惟其与天地万物一体。所以无不爱也。若无天地万物则体既不具。用无可行。将何以血脉贯通。己欲立而立了何人。己欲达而达了谁某。济施于何处。修己而安之者何物。须是以爱为主。而爱之理包涵万物。方无透漏尔。
天地万物同体而无彼此内外也。惟其与天地万物一体。所以无不爱也。若无天地万物则体既不具。用无可行。将何以血脉贯通。己欲立而立了何人。己欲达而达了谁某。济施于何处。修己而安之者何物。须是以爱为主。而爱之理包涵万物。方无透漏尔。此条。说为仁说要旨。以下诸条。皆由此推之。
所谓性之情条 西山真氏曰。如莲实一段当入于生之性条。退陶先生上 问其曰生之性止互混之疑何也。
曰。欲说仁之名义则不出乎爱。而爱不足以尽仁。则朱子偏专之言所由也。仁与爱两字相对。仁自为性而爱自为情。性自为体而情自为用矣。然其曰生之性云者。就体而专言也。爱之理云者。就体而偏言也。其曰性之情云者。就用而专言也。爱之发云者。就用而偏言也。若其仁之体云者。亦主生之性而对爱之发而言也。何架叠之足疑。曰。仁说既分体用以下。依前彼以爱之理仁之体而言之。则包涵浑全。同为一体。若无天地万物。何处见得其为一体。若其得天地生生之理而为我之心。其流行不息之机。则有感必应。有触必发。无时或间。无处不行。如有源之水遏住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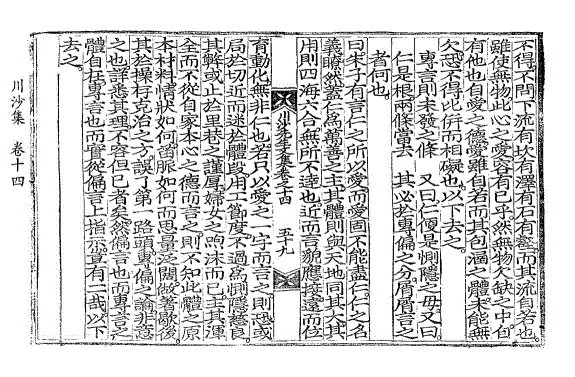 不得。不问下流有坎有泽有石有壑。而其流自若也。虽使无物。此心之爱。容有已乎。然无物欠缺之中。自有他也自爱之德。爱虽自若而其包涵之体。未能无欠。恐不得比并而相碍也。以下去之。
不得。不问下流有坎有泽有石有壑。而其流自若也。虽使无物。此心之爱。容有已乎。然无物欠缺之中。自有他也自爱之德。爱虽自若而其包涵之体。未能无欠。恐不得比并而相碍也。以下去之。专言则未发之条 又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仁是根。两条当去 其必于专偏之分。屑屑言之者何也。
曰。朱子有言仁之所以爱。而爱固不能尽仁。仁之名义瞭然。盖仁为万善之主。其体则与天地同其大。其用则四海六合。无所不达也。近而言貌应接。远而位育动化。无非仁也。若只以爱之一字而言之。则恐或局于切近而迷于体段。用工节度。不过为恻隐慈良。其弊或止于里巷之谨厚。妇女之喣沫而已。主其浑全而不从自家本心之德而言之。则不知此体之原本材料。情状如何。苗脉如何而思量泛阔。做著歇后。其于操存克治之方。误了第一路头。专偏之论。非意之也。详悉其理。不容但已者矣。然偏言也而专言之体自在。专言也而实从偏言上指示。岂有二哉。以下去之。
川沙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第 493L 页
 仁说图
仁说图삽화 새창열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