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x 页
云溪漫稿卷之七
序
序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2H 页
 送外舅直庵先生游枫岳序
送外舅直庵先生游枫岳序古人之乐观于名山者何哉。岂非磅礴扶舆之气。清丽秀特之状。足令人壮心快目。涤尘坋而纳烟霞。恢胸襟而挹爽灏耶。东海之东。有山焉。其名曰金刚。其峰一万二千。其状神剜鬼雕。争奇竞秀。变态不穷。天下之名山。盖莫能尚。麻鞋者日陟焉。肩舆者月迈焉。前者才去。后者复来。而能以金刚之游。涤尘坋恢胸襟者。寂乎未闻。甚矣观山之无益于人也。然非山之过也。观者之不以理观之而以物观之也。何者。以物观之。则山自山我自我。以理观之。则物我无异。而可取以相资也。虽然观理有术。必本于学。盖学者由内而验于外者也。山者自外而资于内者也。故必先博学明理。以立其本。使吾之方寸洞然。左右逢原。则虽一拳石一撮土之微。亦必有契悟于心。况其佳山丽水之蕴至理含灵异者耶。惟我先生。闭户读书三十年玆矣。一朝俶装戒驭。将作枫岳之游。岂学博理明。积于内者既至。而将以验于外者耶。吾固知陟彼之际。始则循序渐进而识升高自卑之义。中则硬着脚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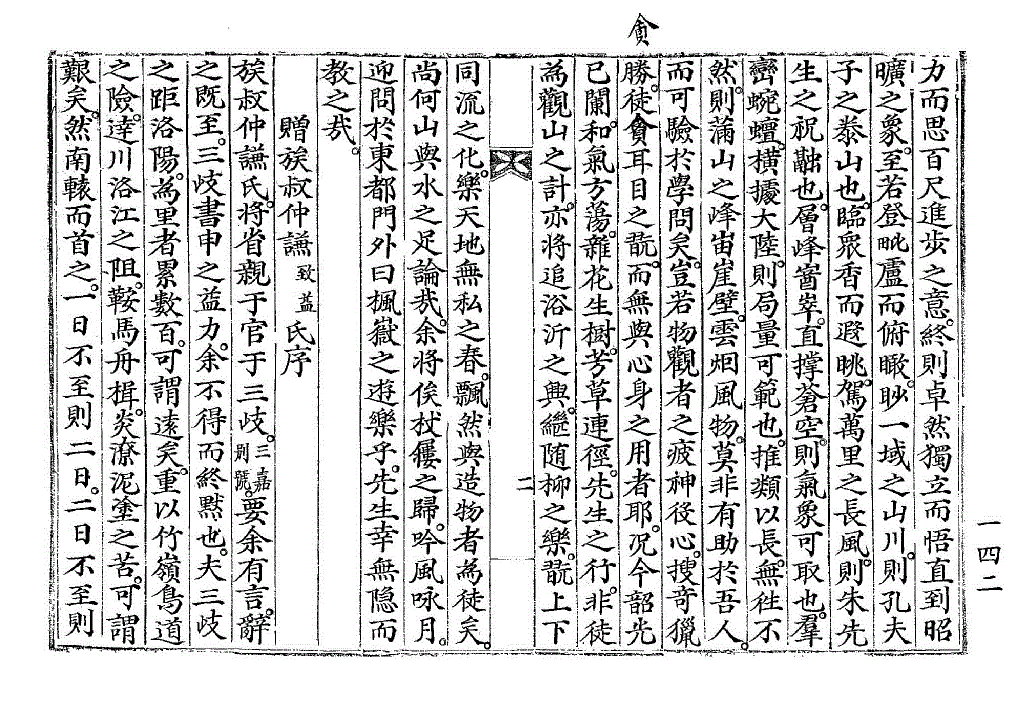 力而思百尺进步之意。终则卓然独立而悟直到昭旷之象。至若登毗卢而俯瞰。眇一域之山川。则孔夫子之泰山也。临众香而遐眺。驾万里之长风。则朱先生之祝融也。层峰𡺚崒。直撑苍空。则气象可取也。群峦蜿蟺。横据大陆。则局量可范也。推类以长。无往不然。则满山之峰岫崖壁。云烟风物。莫非有助于吾人。而可验于学问矣。岂若物观者之疲神役心。搜奇猎胜。徒贪耳目之玩。而无与心身之用者耶。况今韶光已阑。和气方荡。杂花生树。芳草连径。先生之行。非徒为观山之计。亦将追浴沂之兴。继随柳之乐。玩上下同流之化。乐天地无私之春。飘然与造物者为徒矣。尚何山与水之足论哉。余将俟杖屦之归。吟风咏月。迎问于东都门外曰枫岳之游乐乎。先生幸无隐而教之哉。
力而思百尺进步之意。终则卓然独立而悟直到昭旷之象。至若登毗卢而俯瞰。眇一域之山川。则孔夫子之泰山也。临众香而遐眺。驾万里之长风。则朱先生之祝融也。层峰𡺚崒。直撑苍空。则气象可取也。群峦蜿蟺。横据大陆。则局量可范也。推类以长。无往不然。则满山之峰岫崖壁。云烟风物。莫非有助于吾人。而可验于学问矣。岂若物观者之疲神役心。搜奇猎胜。徒贪耳目之玩。而无与心身之用者耶。况今韶光已阑。和气方荡。杂花生树。芳草连径。先生之行。非徒为观山之计。亦将追浴沂之兴。继随柳之乐。玩上下同流之化。乐天地无私之春。飘然与造物者为徒矣。尚何山与水之足论哉。余将俟杖屦之归。吟风咏月。迎问于东都门外曰枫岳之游乐乎。先生幸无隐而教之哉。赠族叔仲谦(致益)氏序
族叔仲谦氏。将省亲于官于三岐。(三嘉别号。)要余有言。辞之既至。三岐书申之益力。余不得而终默也。夫三岐之距洛阳。为里者累数百。可谓远矣。重以竹岭鸟道之险。达川洛江之阻。鞍马舟楫。炎潦泥涂之苦。可谓艰矣。然南辕而首之。一日不至则二日。二日不至则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3H 页
 三日十日不已。则居然而至矣。虽进乎此。而南而粤北而燕。苟不已无不至。特患无其志及虽有志而懈而止耳。吾党之学道者亦然。望走乎邹鲁。标准乎洛闽。下学上达。进进不已。其不至者未之有也。乍进而旋退。半上而落下。其至者亦未之有也。仲谦氏发轫最早。求道甚锐。吾固知其有志。而又不懈而止焉者。虽然传不云乎。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非可以一时慷慨之志。少年刚锐之气。躐超而骤至也。其可恃此而自安乎。用是为赠。亦以自警。
三日十日不已。则居然而至矣。虽进乎此。而南而粤北而燕。苟不已无不至。特患无其志及虽有志而懈而止耳。吾党之学道者亦然。望走乎邹鲁。标准乎洛闽。下学上达。进进不已。其不至者未之有也。乍进而旋退。半上而落下。其至者亦未之有也。仲谦氏发轫最早。求道甚锐。吾固知其有志。而又不懈而止焉者。虽然传不云乎。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非可以一时慷慨之志。少年刚锐之气。躐超而骤至也。其可恃此而自安乎。用是为赠。亦以自警。送徐君受(命膺)使日本序
倭天下之狡奴也。跨海而邻于我。粤昔壬癸之际。狡焉为蛇豕。荐食我八域。我方剪焉。而奴亦创甚。又挟狡款于我。我力不能拒。遂有泛海之役。此信使之始也。今 上癸未。徐君受以副提学充上价。将行。要余有言。余曰。自夫狡奴之输平。而南边不耸。海波不惊。且数百年所。人遂不以奴为意。然狎虎豹傍虺蛇。而久保其无事。余莫之知也。昔韩昌黎送殷员外使回鹘。叹其无几微见于言面。嗟夫。使乎之责。岂止于不见几微而已乎。陆生之使南越也。能令黄屋左纛之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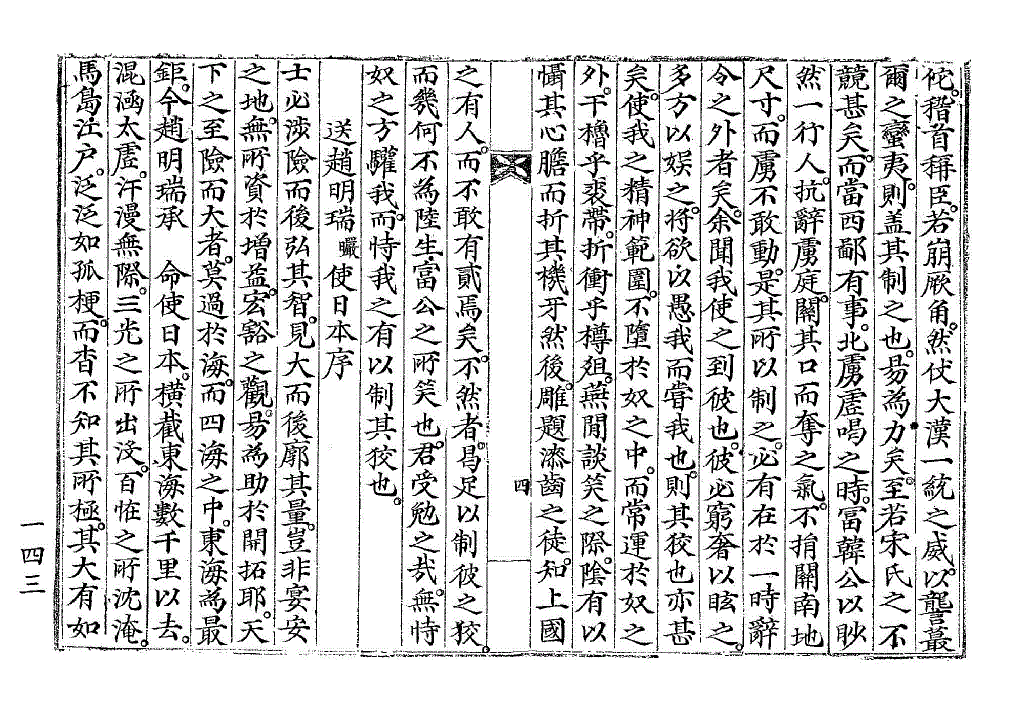 佗。稽首称臣。若崩厥角。然仗大汉一统之威。以詟蕞尔之蛮夷。则盖其制之也。易为力矣。至若宋氏之不竞甚矣。而当西鄙有事。北虏虚喝之时。富韩公以眇然一行人。抗辞虏庭。关其口而夺之气。不捐关南地尺寸。而虏不敢动。是其所以制之。必有在于一时辞令之外者矣。余闻我使之到彼也。彼必穷奢以眩之。多方以娱之。将欲以愚我而尝我也。则其狡也亦甚矣。使我之精神范围。不堕于奴之中。而常运于奴之外。干橹乎裘带。折冲乎樽俎。燕閒谈笑之际。阴有以慑其心胆而折其机牙然后。雕题漆齿之徒。知上国之有人。而不敢有贰焉矣。不然者。曷足以制彼之狡。而几何不为陆生,富公之所笑也。君受勉之哉。无恃奴之方驩我。而恃我之有以制其狡也。
佗。稽首称臣。若崩厥角。然仗大汉一统之威。以詟蕞尔之蛮夷。则盖其制之也。易为力矣。至若宋氏之不竞甚矣。而当西鄙有事。北虏虚喝之时。富韩公以眇然一行人。抗辞虏庭。关其口而夺之气。不捐关南地尺寸。而虏不敢动。是其所以制之。必有在于一时辞令之外者矣。余闻我使之到彼也。彼必穷奢以眩之。多方以娱之。将欲以愚我而尝我也。则其狡也亦甚矣。使我之精神范围。不堕于奴之中。而常运于奴之外。干橹乎裘带。折冲乎樽俎。燕閒谈笑之际。阴有以慑其心胆而折其机牙然后。雕题漆齿之徒。知上国之有人。而不敢有贰焉矣。不然者。曷足以制彼之狡。而几何不为陆生,富公之所笑也。君受勉之哉。无恃奴之方驩我。而恃我之有以制其狡也。送赵明瑞(曮)使日本序
士必涉险而后弘其智。见大而后廓其量。岂非宴安之地。无所资于增益。宏豁之观。易为助于开拓耶。天下之至险而大者。莫过于海。而四海之中。东海为最钜。今赵明瑞承 命使日本。横截东海数千里以去。混涵太虚。汗漫无际。三光之所出没。百怪之所沈淹。马岛,江户。泛泛如孤梗。而杳不知其所极。其大有如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4H 页
 此者。冲飙荡激。怒波屃赑。坤轴骇转。日车愁翻。阳侯天吴。恍惚左右。万斛千帆。颠倒须臾。其险有如此者。是知炮车飓母之不可不慎其候也。峨樯巨缆之不可不谨其备也。岂若一带水然哉。可以轻试而倖涉也。吾知明瑞于是行。必有得矣。其将弘其智而廓其量矣乎。虽然天下之事。不有险且大于东海者乎。其为变也无穷。其为忧也无涯。安危所关。非特一苇之沈浮也。风波所荡。非特万顷之澒洞也。苟非智足以经天下之务。量足以容天下之物。则亦何以济天下之至险而办天下之大事乎。欧阳永叔赞韩魏公。云当大事决大疑。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易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若魏公者非耶。明瑞恢闳有器局。骎骎然见用于世。方来之责未艾也。今余之所期望。不止善于济沧海而已。惟明瑞勉之哉。
此者。冲飙荡激。怒波屃赑。坤轴骇转。日车愁翻。阳侯天吴。恍惚左右。万斛千帆。颠倒须臾。其险有如此者。是知炮车飓母之不可不慎其候也。峨樯巨缆之不可不谨其备也。岂若一带水然哉。可以轻试而倖涉也。吾知明瑞于是行。必有得矣。其将弘其智而廓其量矣乎。虽然天下之事。不有险且大于东海者乎。其为变也无穷。其为忧也无涯。安危所关。非特一苇之沈浮也。风波所荡。非特万顷之澒洞也。苟非智足以经天下之务。量足以容天下之物。则亦何以济天下之至险而办天下之大事乎。欧阳永叔赞韩魏公。云当大事决大疑。垂绅正笏。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易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若魏公者非耶。明瑞恢闳有器局。骎骎然见用于世。方来之责未艾也。今余之所期望。不止善于济沧海而已。惟明瑞勉之哉。送金仲佑(相翊)使日本从事序
我 朝以文为治。不竞于武。南辱于倭而有 二陵之变。北创于虏而有城下之盟。此皆万世臣子之雠。而人心易狃。义理不明。痛定疮息。浸以相忘。后来诸先生。倡大义而号于世曰夷虏雠也。臣仆羞也。自是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4L 页
 妇人孺子。皆知复雠雪耻之为不可忘。含冤忍痛之为不得已。虽国小力弱。不能有为。而明天理正人心之功。可谓盛矣。独怪夫交倭一事。则未尝有严辞力斥。以明其不可者何也。岂诸先生适当丙丁之后。目见冠屦之倒。伦常之斁。尽气力以撑拄之。而龙蛇已事。有不暇及者耶。或又以为今之酋。非秀吉之种。其和也无不可。则独不观夫南渡乾淳之世乎。逆亮之毙。而金酋之立者。若非阿骨之裔。则朱夫子复雪之义。将无所施。而东窗讲和之论。为不可易欤。余尝筮仕守 靖陵寝。其西即 宣陵也。其间云烟郁结。常若有不平之气。每当夏秋之际。江波怒吼。林木悲鸣。恍疑 陟降之灵。犹赫怒于冥冥也。他日吾邦兵强而力裕。揭春秋之义而兴复雠之师。则吾知义旗之指。不先于北而先于南矣。嗟乎吾不得以此义仰质于诸先生也。余友金仲佑有志士也。以从事膺 命赴日本。余知今日之行。非仲佑所乐也。虽然吾于仲佑之行。别有感焉。昔莒嫠妇欲报其子雠。以纺度城而去之。待晋师而投诸外。使师缒而登而莒遂溃焉。匹妇励志。犹尚如此。况明义识务之君子乎。试以君行之所经历。某港可泊。某岛可伏。某处坚而某处瑕。
妇人孺子。皆知复雠雪耻之为不可忘。含冤忍痛之为不得已。虽国小力弱。不能有为。而明天理正人心之功。可谓盛矣。独怪夫交倭一事。则未尝有严辞力斥。以明其不可者何也。岂诸先生适当丙丁之后。目见冠屦之倒。伦常之斁。尽气力以撑拄之。而龙蛇已事。有不暇及者耶。或又以为今之酋。非秀吉之种。其和也无不可。则独不观夫南渡乾淳之世乎。逆亮之毙。而金酋之立者。若非阿骨之裔。则朱夫子复雪之义。将无所施。而东窗讲和之论。为不可易欤。余尝筮仕守 靖陵寝。其西即 宣陵也。其间云烟郁结。常若有不平之气。每当夏秋之际。江波怒吼。林木悲鸣。恍疑 陟降之灵。犹赫怒于冥冥也。他日吾邦兵强而力裕。揭春秋之义而兴复雠之师。则吾知义旗之指。不先于北而先于南矣。嗟乎吾不得以此义仰质于诸先生也。余友金仲佑有志士也。以从事膺 命赴日本。余知今日之行。非仲佑所乐也。虽然吾于仲佑之行。别有感焉。昔莒嫠妇欲报其子雠。以纺度城而去之。待晋师而投诸外。使师缒而登而莒遂溃焉。匹妇励志。犹尚如此。况明义识务之君子乎。试以君行之所经历。某港可泊。某岛可伏。某处坚而某处瑕。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5H 页
 某路险而某路夷。审度而详记之。瞭然如马援之米山。曹翰之燕图。归以藏之。以俟后日。则安知其不按而行师。如莒妇量城之纺者乎。于其行。聊以是为赠。
某路险而某路夷。审度而详记之。瞭然如马援之米山。曹翰之燕图。归以藏之。以俟后日。则安知其不按而行师。如莒妇量城之纺者乎。于其行。聊以是为赠。梅古堂集序
余尝阅晋山世稿。自通亭以下。至于私淑斋,醉竹诸公。圭璋炳烺。以鸣 国家之盛。何姜氏之多才也。近世有菊窝公。以词藻擅场。一时能文之士。皆自以为不及。而竟屈于荫途。人皆惜其有才无命云。美叔。菊窝公之季子也。早孤贫窭甚。而能自力为文辞。疏宕有逸气。诗亦遒健可喜。假年以充之。可以接武世稿。而有才无命。又有甚于菊窝公。悲夫。美叔于余为中表叔。生同庚少同学。长而同研。以余钝根狷姿。世无好者。而独美叔相与之深。每见一篇。为之讽读不倦。又为称道于朋友。以至科甲得丧之际。辄亦舍己而推余。余观末俗猜忮。往往于其所亲厚愈甚。平居欢好。昵昵翕翕。及其声名稍相轧。则必巧诋而暗挤。一朝利害。仅如毫发比。或至操戈而争先。若美叔之为。可谓贤于人远矣。所交游不甚广。而要皆洛下知名士。至今相与道美叔。未尝不恻怆咨嗟。至于泫眦。其所以得此于交际之间者。岂以声音笑貌为哉。尹学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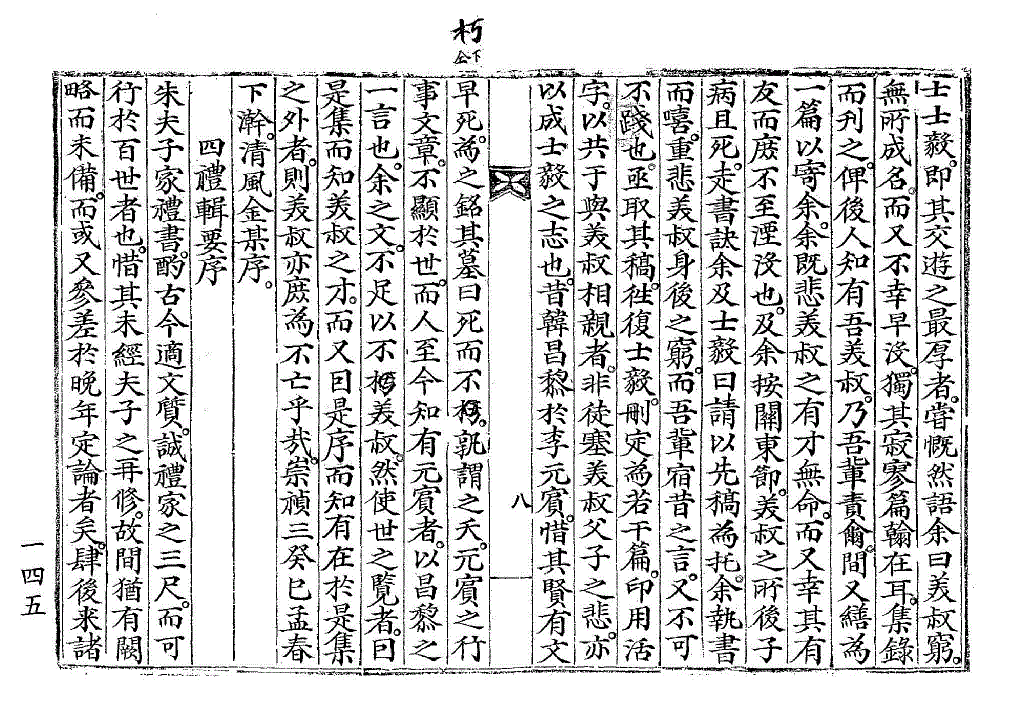 士士毅。即其交游之最厚者。尝慨然语余曰美叔穷。无所成名。而又不幸早没。独其寂寥篇翰在耳。集录而刊之。俾后人知有吾美叔。乃吾辈责尔。间又缮为一篇以寄余。余既悲美叔之有才无命。而又幸其有友而庶不至湮没也。及余按关东节。美叔之所后子病且死。走书诀余及士毅曰请以先稿为托。余执书而嘻。重悲美叔身后之穷。而吾辈宿昔之言。又不可不践也。亟取其稿。往复士毅。删定为若干篇。印用活字。以共于与美叔相亲者。非徒塞美叔父子之悲。亦以成士毅之志也。昔韩昌黎于李元宾。惜其贤有文早死。为之铭其墓曰死而不朽。孰谓之夭。元宾之行事文章。不显于世。而人至今知有元宾者。以昌黎之一言也。余之文。不足以不朽美叔。然使世之览者。因是集而知美叔之才。而又因是序而知有在于是集之外者。则美叔亦庶为不亡乎哉。崇祯三癸巳孟春下浣。清风金某序。
士士毅。即其交游之最厚者。尝慨然语余曰美叔穷。无所成名。而又不幸早没。独其寂寥篇翰在耳。集录而刊之。俾后人知有吾美叔。乃吾辈责尔。间又缮为一篇以寄余。余既悲美叔之有才无命。而又幸其有友而庶不至湮没也。及余按关东节。美叔之所后子病且死。走书诀余及士毅曰请以先稿为托。余执书而嘻。重悲美叔身后之穷。而吾辈宿昔之言。又不可不践也。亟取其稿。往复士毅。删定为若干篇。印用活字。以共于与美叔相亲者。非徒塞美叔父子之悲。亦以成士毅之志也。昔韩昌黎于李元宾。惜其贤有文早死。为之铭其墓曰死而不朽。孰谓之夭。元宾之行事文章。不显于世。而人至今知有元宾者。以昌黎之一言也。余之文。不足以不朽美叔。然使世之览者。因是集而知美叔之才。而又因是序而知有在于是集之外者。则美叔亦庶为不亡乎哉。崇祯三癸巳孟春下浣。清风金某序。四礼辑要序
朱夫子家礼书。酌古今适文质。诚礼家之三尺。而可行于百世者也。惜其未经夫子之再修。故间犹有阙略而未备。而或又参差于晚年定论者矣。肆后来诸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6H 页
 贤。或补缀之。或订正之。其杂见于答问者。又皆推明是书。以尽夫常变之节。然其所损益从违者。未知尽得夫子之意否乎。而况诸书浩瀚。同异纷互。学者病难遍考。考之又无所折衷。则于是乎各以其意。各行其所知。虽曰同祖乎家礼。而亦不免多歧之惑矣。噫。夫子之意。虽不可复识。苟一主乎家礼。而质以晚年之论。参以诸贤之书。阙其疑而慎行其馀。亦庶几寡过矣乎。愚于礼学之无素。及遭大故。荒迷颠错。有不胜其悔者。始乃取家礼而读之。仍及乎古今诸书。则如堕烟雾。茫然不知所适。反覆参究。盖亦有年然后。窃不自揆。手辑一编。以家礼本文为纲。节取古今诸书。逐条分注于下。名曰四礼辑要。非以求异乎他书。要在可行而已。故虽在本文。而晚年定论所否者不书。若诸书同异之说疑者不书。书者斯可行已。其庶几寡过矣乎。是未敢知也。而謏闻浅识。拣别不明。诚莫逃僭汰之罪。第用藏之巾笥。备一家之私考。非敢共之于人云尔。
贤。或补缀之。或订正之。其杂见于答问者。又皆推明是书。以尽夫常变之节。然其所损益从违者。未知尽得夫子之意否乎。而况诸书浩瀚。同异纷互。学者病难遍考。考之又无所折衷。则于是乎各以其意。各行其所知。虽曰同祖乎家礼。而亦不免多歧之惑矣。噫。夫子之意。虽不可复识。苟一主乎家礼。而质以晚年之论。参以诸贤之书。阙其疑而慎行其馀。亦庶几寡过矣乎。愚于礼学之无素。及遭大故。荒迷颠错。有不胜其悔者。始乃取家礼而读之。仍及乎古今诸书。则如堕烟雾。茫然不知所适。反覆参究。盖亦有年然后。窃不自揆。手辑一编。以家礼本文为纲。节取古今诸书。逐条分注于下。名曰四礼辑要。非以求异乎他书。要在可行而已。故虽在本文。而晚年定论所否者不书。若诸书同异之说疑者不书。书者斯可行已。其庶几寡过矣乎。是未敢知也。而謏闻浅识。拣别不明。诚莫逃僭汰之罪。第用藏之巾笥。备一家之私考。非敢共之于人云尔。云溪漫稿卷之七
记
岁寒亭记
时之变物也无常。而物之有常者。不以时变。烈火燎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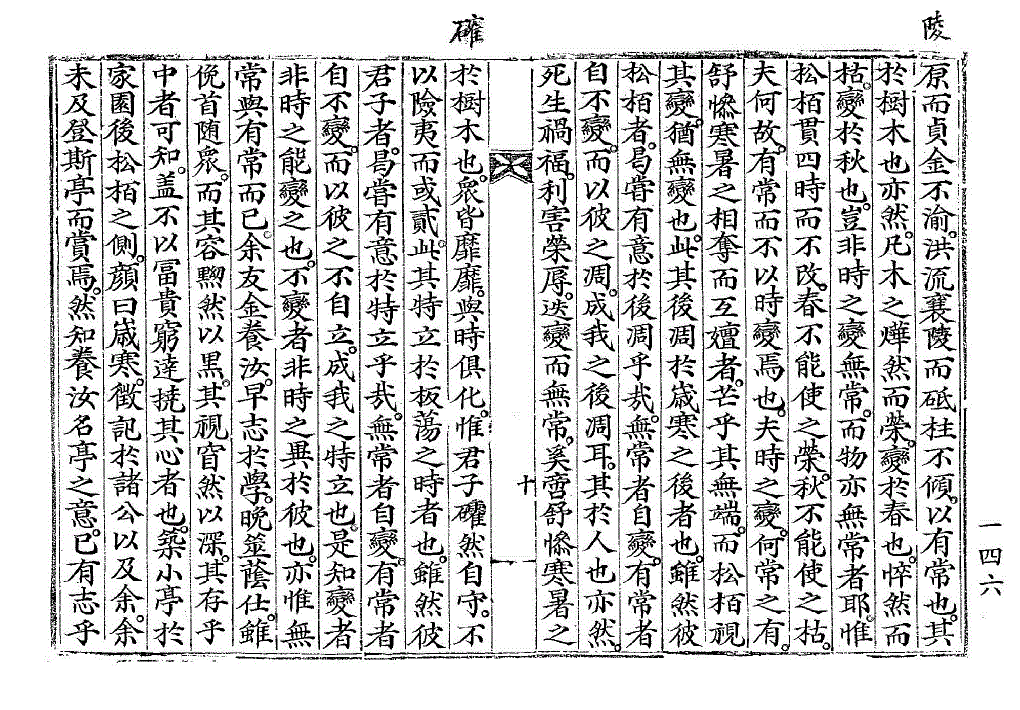 原而贞金不渝。洪流襄陵而砥柱不倾。以有常也。其于树木也亦然。凡木之烨然而荣。变于春也。悴然而枯。变于秋也。岂非时之变无常。而物亦无常者耶。惟松柏贯四时而不改。春不能使之荣。秋不能使之枯。夫何故。有常而不以时变焉也。夫时之变。何常之有。舒惨寒暑之相夺而互嬗者。芒乎其无端。而松柏视其变。犹无变也。此其后凋于岁寒之后者也。虽然彼松柏者。曷尝有意于后凋乎哉。无常者自变。有常者自不变。而以彼之凋。成我之后凋耳。其于人也亦然。死生祸福。利害荣辱。迭变而无常。奚啻舒惨寒暑之于树木也。众皆靡靡。与时俱化。惟君子确然自守。不以险夷而或贰。此其特立于板荡之时者也。虽然彼君子者。曷尝有意于特立乎哉。无常者自变。有常者自不变。而以彼之不自立。成我之特立也。是知变者非时之能变之也。不变者非时之异于彼也。亦惟无常与有常而已。余友金养汝。早志于学。晚筮荫仕。虽俛首随众。而其容黝然以黑。其视窅然以深。其存乎中者可知。盖不以富贵穷达挠其心者也。筑小亭于家园后松柏之侧。颜曰岁寒。徵记于诸公以及余。余未及登斯亭而赏焉。然知养汝名亭之意。已有志乎
原而贞金不渝。洪流襄陵而砥柱不倾。以有常也。其于树木也亦然。凡木之烨然而荣。变于春也。悴然而枯。变于秋也。岂非时之变无常。而物亦无常者耶。惟松柏贯四时而不改。春不能使之荣。秋不能使之枯。夫何故。有常而不以时变焉也。夫时之变。何常之有。舒惨寒暑之相夺而互嬗者。芒乎其无端。而松柏视其变。犹无变也。此其后凋于岁寒之后者也。虽然彼松柏者。曷尝有意于后凋乎哉。无常者自变。有常者自不变。而以彼之凋。成我之后凋耳。其于人也亦然。死生祸福。利害荣辱。迭变而无常。奚啻舒惨寒暑之于树木也。众皆靡靡。与时俱化。惟君子确然自守。不以险夷而或贰。此其特立于板荡之时者也。虽然彼君子者。曷尝有意于特立乎哉。无常者自变。有常者自不变。而以彼之不自立。成我之特立也。是知变者非时之能变之也。不变者非时之异于彼也。亦惟无常与有常而已。余友金养汝。早志于学。晚筮荫仕。虽俛首随众。而其容黝然以黑。其视窅然以深。其存乎中者可知。盖不以富贵穷达挠其心者也。筑小亭于家园后松柏之侧。颜曰岁寒。徵记于诸公以及余。余未及登斯亭而赏焉。然知养汝名亭之意。已有志乎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7H 页
 有常者。一此不变焉。则他日岁寒之操。亦庶几不负斯亭者。故为是说以勉之。
有常者。一此不变焉。则他日岁寒之操。亦庶几不负斯亭者。故为是说以勉之。九龙亭记
鸭水西流。未至湾府治数里而汇为渊。旧传九龙攸居。遂以名厥有。穹壁侧立百尺。上平为台。下插无垠。余尝尹湾。登玆而览焉。深潭黝黑。不可狎视。尚疑神物閟焉。虬松郁然荫映古祠。水旱之所祷也。北望松鹘,金石诸山。隔江竦峙。风沙渺漭。有万里之势。南则短冈平畴。窈窕明媚。州人之所游嬉。关塞之雄远。丘壑之闲靓。兼有其胜矣。欣然赏之。欲置亭其上。未果而去。今湾尹洪侯幼直之行也。余以是语之。幼直慨然曰昔吾祖参判公之莅玆州也。为亭于是。而久而墟焉。是吾责也。未几走书以告其成。曰室一架而轩四面。又筑射亭其傍。皆按吾祖之旧而稍拓之矣。子有前言。盍有以识之。余悦是举也。以为参判公之刱之也。实古人之先获。而今侯之肯构。能趾其美。是不可以无传也。或曰疆索之务。城池与甲兵已矣。一亭之兴废。奚足为重轻哉。余曰不然。不见夫羊叔子,杜元凯之为荆州矣乎。与僚佐登岘首。日置酒为乐。风流人物。照映一世。而后来礼功盛烈。直与江汉同流。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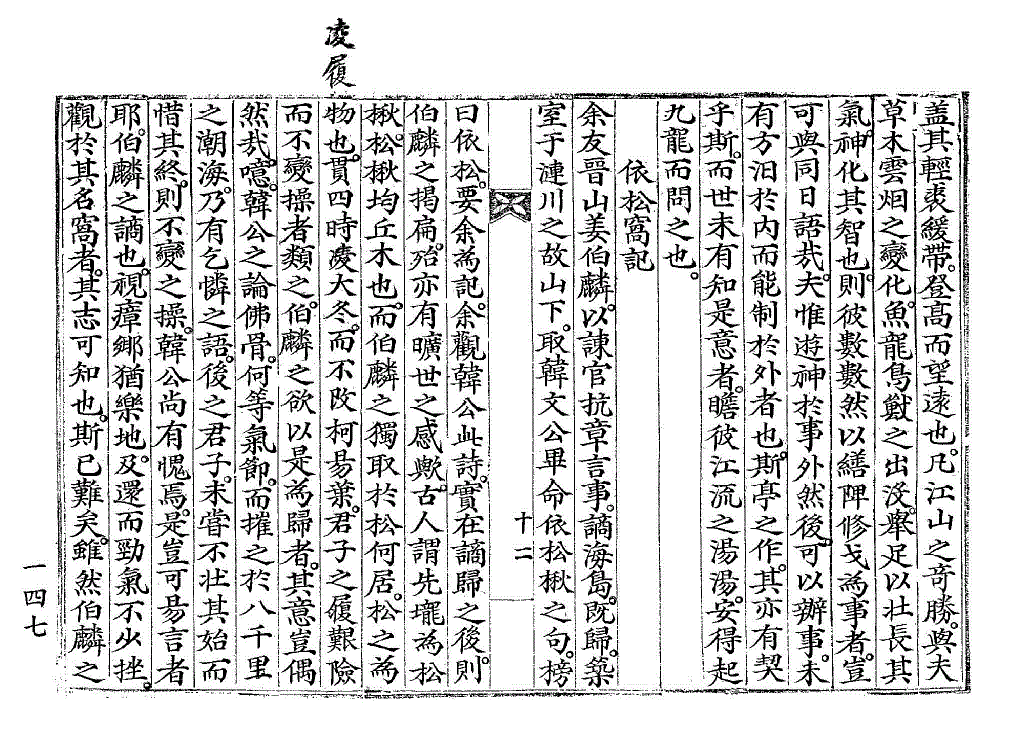 盖其轻裘缓带。登高而望远也。凡江山之奇胜。与夫草木云烟之变化。鱼龙鸟兽之出没。举足以壮长其气。神化其智也。则彼数数然以缮陴修戈为事者。岂可与同日语哉。夫惟游神于事外然后。可以办事。未有方汨于内而能制于外者也。斯亭之作。其亦有契乎斯。而世未有知是意者。瞻彼江流之汤汤。安得起九龙而问之也。
盖其轻裘缓带。登高而望远也。凡江山之奇胜。与夫草木云烟之变化。鱼龙鸟兽之出没。举足以壮长其气。神化其智也。则彼数数然以缮陴修戈为事者。岂可与同日语哉。夫惟游神于事外然后。可以办事。未有方汨于内而能制于外者也。斯亭之作。其亦有契乎斯。而世未有知是意者。瞻彼江流之汤汤。安得起九龙而问之也。依松窝记
余友晋山姜伯麟。以谏官抗章言事。谪海岛。既归。筑室于涟川之故山下。取韩文公毕命依松楸之句。榜曰依松。要余为记。余观韩公此诗。实在谪归之后。则伯麟之揭扁。殆亦有旷世之感欤。古人谓先垄为松楸。松楸均丘木也。而伯麟之独取于松何居。松之为物也。贯四时凌大冬。而不改柯易叶。君子之履艰险而不变操者类之。伯麟之欲以是为归者。其意岂偶然哉。噫。韩公之论佛骨。何等气节。而摧之于八千里之潮海。乃有乞怜之语。后之君子。未尝不壮其始而惜其终。则不变之操。韩公尚有愧焉。是岂可易言者耶。伯麟之谪也。视瘴乡犹乐地。及还而劲气不少挫。观于其名窝者。其志可知也。斯已难矣。虽然伯麟之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8H 页
 谠言。远逊于佛骨。薄窜未及于潮阳。其所成就所阅历。视韩公。杳然斯下矣。譬之木焉。虽不至于望秋而零。而亦未定其经大冬而不变也。无遽沾沾乎其所已能。而益养其浩然刚大之气。虽极天下之险。不足以变其操然后。方可无愧于斯扁。伯麟其亦有意否乎。且韩公既作诗。而旋出为世用。事为多卓卓可记。今伯麟之才学。亦非终老于林下者。余将以其处而卜其出。彼百围之松。终为大厦之具者。亦惟养之有素耳。伯麟勉之哉。
谠言。远逊于佛骨。薄窜未及于潮阳。其所成就所阅历。视韩公。杳然斯下矣。譬之木焉。虽不至于望秋而零。而亦未定其经大冬而不变也。无遽沾沾乎其所已能。而益养其浩然刚大之气。虽极天下之险。不足以变其操然后。方可无愧于斯扁。伯麟其亦有意否乎。且韩公既作诗。而旋出为世用。事为多卓卓可记。今伯麟之才学。亦非终老于林下者。余将以其处而卜其出。彼百围之松。终为大厦之具者。亦惟养之有素耳。伯麟勉之哉。镜浦台重修记
我东山水之胜名天下。而岭东为最。岭东之胜著名者十数。而镜浦台为最。此不易之评也。余尝衔关东从事之 命。踰大岭并海而行。日接于前者。愈奇愈伟。动心骇目。而至所谓镜浦台而观止焉。平湖潋滟。环三十里。弯以沙堤。莹如白雪。其外则银海浩渺。与天无际。然湖与海。各擅其胜。不相为谋。而台则一举目而兼收焉。斯其所以最胜者欤。尹伯常,洪叔行。登枫岳探八景。蹑余于水城。篝灯品诸胜。以镜浦台,三日浦相上下。不能定。余曰三日以幽眇胜。如费长房入白玉壶。窅然令人迷。镜浦以奇旷胜。如周穆王登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8L 页
 化人宫。恍然令人浮。此其格局小大之别也。二友以余言为然云。台旧有阁。屡废屡兴。而近又几于废矣。李侍郎圣鲁撤宰班分岭符才数月。政成事简。览台而喟然曰是吾责也。于是易其材之腐瓦之缺者。鲜其漫正其欹。而湖海之观。居然添一胜矣。昔人以杭之西湖。譬人之有眉目。而白少傅,苏长公。先后贲饰之。游赏之趣。啸咏之乐。风流文采。照映千载。今镜浦之胜。奚止西湖。而玆阁之重新。又足以润色湖山。如修眉明眸。更施妍妆。则侍郎之为。其亦闻二公之风者欤。适余又忝道伯。喜是役也。为之记如此。异日登临。尚可凭画槛展遐瞩。而重理山水之评也。
化人宫。恍然令人浮。此其格局小大之别也。二友以余言为然云。台旧有阁。屡废屡兴。而近又几于废矣。李侍郎圣鲁撤宰班分岭符才数月。政成事简。览台而喟然曰是吾责也。于是易其材之腐瓦之缺者。鲜其漫正其欹。而湖海之观。居然添一胜矣。昔人以杭之西湖。譬人之有眉目。而白少傅,苏长公。先后贲饰之。游赏之趣。啸咏之乐。风流文采。照映千载。今镜浦之胜。奚止西湖。而玆阁之重新。又足以润色湖山。如修眉明眸。更施妍妆。则侍郎之为。其亦闻二公之风者欤。适余又忝道伯。喜是役也。为之记如此。异日登临。尚可凭画槛展遐瞩。而重理山水之评也。正斋记
传曰君子大居正。夫正者。天地之常道。生民之大法也。存乎天者。阴阳寒暑之运。风雨霜露之化。无一物之不正也。存乎人者。视听言动之则。父子君臣之伦。无一事之不正也。是以君子之道。以居正为大。治心修身。咸以其正。举而措之于正家正国。则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者也。三微以降。正道浸熄。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而世道以之不正。私欲日炽。天理日湮。而人心以之不正。及其反覆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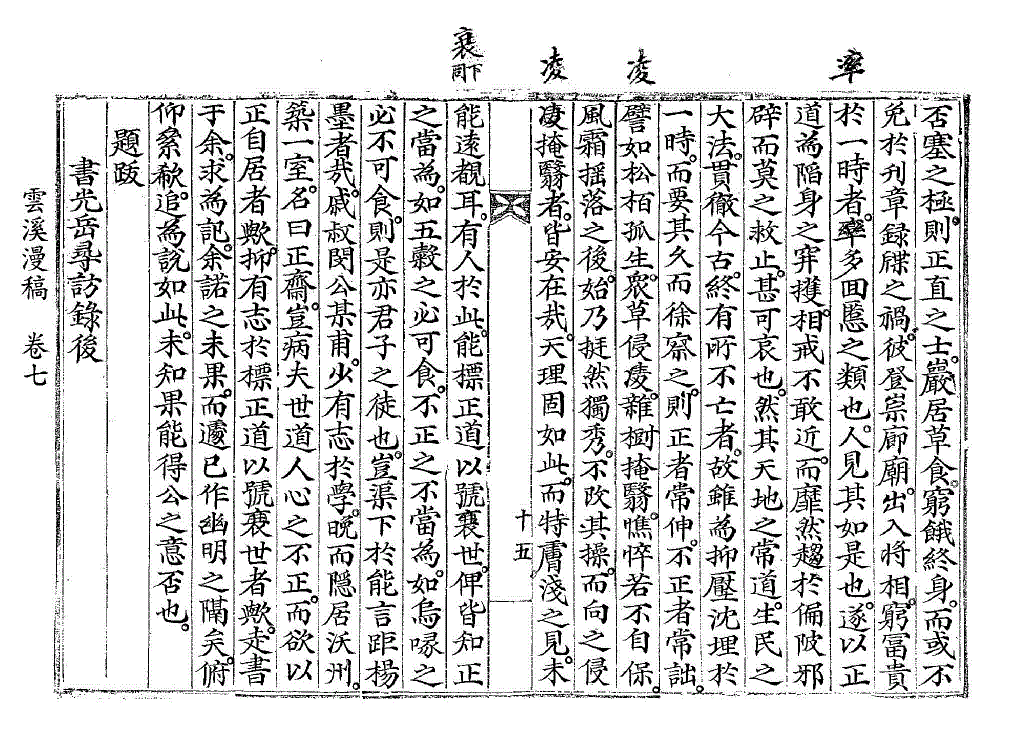 否塞之极。则正直之士。岩居草食。穷饿终身。而或不免于刊章录牒之祸。彼登崇廊庙。出入将相。穷富贵于一时者。率多回慝之类也。人见其如是也。遂以正道为陷身之阱擭。相戒不敢近。而靡然趋于偏陂邪辟而莫之救止。甚可哀也。然其天地之常道。生民之大法。贯彻今古。终有所不亡者。故虽为抑压沈埋于一时。而要其久而徐察之。则正者常伸。不正者常诎。譬如松柏孤生。众草侵凌。杂树掩翳。憔悴若不自保。风霜摇落之后。始乃挺然独秀。不改其操。而向之侵凌掩翳者。皆安在哉。天理固如此。而特肤浅之见。未能远睹耳。有人于此。能标正道以号衰世。俾皆知正之当为。如五谷之必可食。不正之不当为。如乌喙之必不可食。则是亦君子之徒也。岂渠下于能言距杨墨者哉。戚叔闵公某甫。少有志于学。晚而隐居沃州。筑一室。名曰正斋。岂病夫世道人心之不正。而欲以正自居者欤。抑有志于标正道以号衰世者欤。走书于余。求为记。余诺之未果。而遽已作幽明之隔矣。俯仰累欷。追为说如此。未知果能得公之意否也。
否塞之极。则正直之士。岩居草食。穷饿终身。而或不免于刊章录牒之祸。彼登崇廊庙。出入将相。穷富贵于一时者。率多回慝之类也。人见其如是也。遂以正道为陷身之阱擭。相戒不敢近。而靡然趋于偏陂邪辟而莫之救止。甚可哀也。然其天地之常道。生民之大法。贯彻今古。终有所不亡者。故虽为抑压沈埋于一时。而要其久而徐察之。则正者常伸。不正者常诎。譬如松柏孤生。众草侵凌。杂树掩翳。憔悴若不自保。风霜摇落之后。始乃挺然独秀。不改其操。而向之侵凌掩翳者。皆安在哉。天理固如此。而特肤浅之见。未能远睹耳。有人于此。能标正道以号衰世。俾皆知正之当为。如五谷之必可食。不正之不当为。如乌喙之必不可食。则是亦君子之徒也。岂渠下于能言距杨墨者哉。戚叔闵公某甫。少有志于学。晚而隐居沃州。筑一室。名曰正斋。岂病夫世道人心之不正。而欲以正自居者欤。抑有志于标正道以号衰世者欤。走书于余。求为记。余诺之未果。而遽已作幽明之隔矣。俯仰累欷。追为说如此。未知果能得公之意否也。云溪漫稿卷之七
题跋
书光岳寻访录后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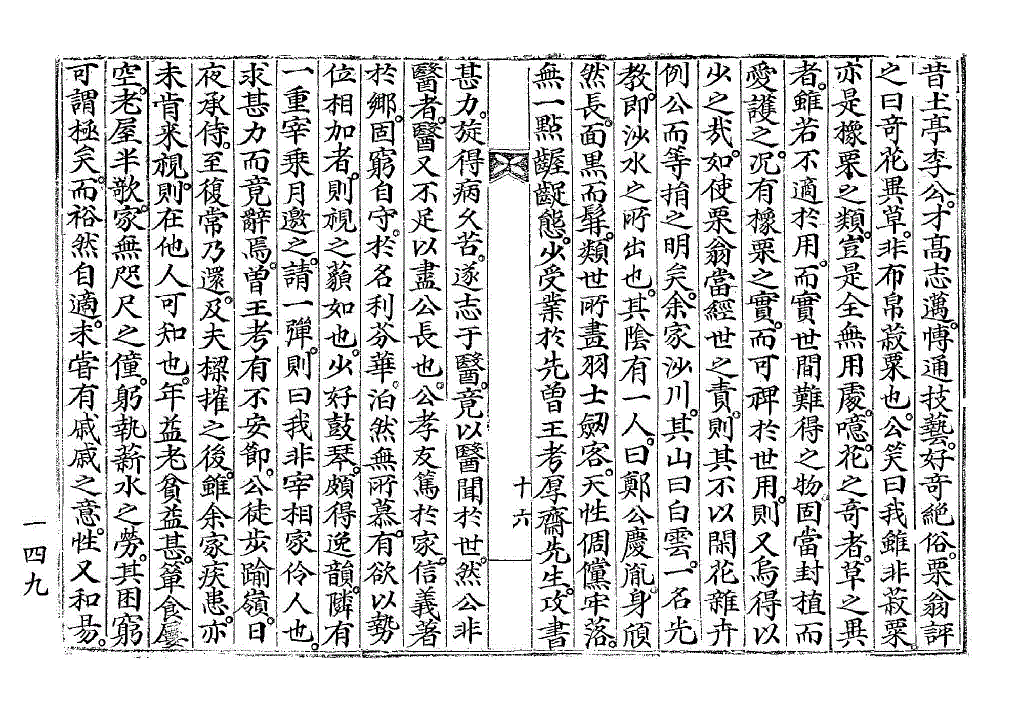 昔土亭李公。才高志迈。博通技艺。好奇绝俗。栗翁评之曰奇花异草。非布帛菽粟也。公笑曰我虽非菽粟。亦是橡栗之类。岂是全无用处。噫。花之奇者。草之异者。虽若不适于用。而实世间难得之物。固当封植而爱护之。况有橡栗之实。而可裨于世用。则又乌得以少之哉。如使栗翁当经世之责。则其不以闲花杂卉例公而等捐之明矣。余家沙川。其山曰白云。一名光教。即沙水之所出也。其阴有一人。曰郑公庆胤。身颀然长。面黑而髯。类世所画羽士剑客。天性倜傥牢落。无一点龌龊态。少受业于先曾王考厚斋先生。攻书甚力。旋得病久苦。遂志于医。竟以医闻于世。然公非医者。医又不足以尽公长也。公孝友笃于家。信义著于乡。固穷自守。于名利芬华。泊然无所慕。有欲以势位相加者。则视之藐如也。少好鼓琴。颇得逸韵。邻有一重宰乘月邀之。请一弹。则曰我非宰相家伶人也。求甚力而竟辞焉。曾王考有不安节。公徒步踰岭。日夜承侍。至复常乃还。及夫梁摧之后。虽余家疾患。亦未肯来视。则在他人可知也。年益老贫益甚。箪食屡空。老屋半欹。家无咫尺之僮。躬执薪水之劳。其困穷可谓极矣。而裕然自适。未尝有戚戚之意。性又和易。
昔土亭李公。才高志迈。博通技艺。好奇绝俗。栗翁评之曰奇花异草。非布帛菽粟也。公笑曰我虽非菽粟。亦是橡栗之类。岂是全无用处。噫。花之奇者。草之异者。虽若不适于用。而实世间难得之物。固当封植而爱护之。况有橡栗之实。而可裨于世用。则又乌得以少之哉。如使栗翁当经世之责。则其不以闲花杂卉例公而等捐之明矣。余家沙川。其山曰白云。一名光教。即沙水之所出也。其阴有一人。曰郑公庆胤。身颀然长。面黑而髯。类世所画羽士剑客。天性倜傥牢落。无一点龌龊态。少受业于先曾王考厚斋先生。攻书甚力。旋得病久苦。遂志于医。竟以医闻于世。然公非医者。医又不足以尽公长也。公孝友笃于家。信义著于乡。固穷自守。于名利芬华。泊然无所慕。有欲以势位相加者。则视之藐如也。少好鼓琴。颇得逸韵。邻有一重宰乘月邀之。请一弹。则曰我非宰相家伶人也。求甚力而竟辞焉。曾王考有不安节。公徒步踰岭。日夜承侍。至复常乃还。及夫梁摧之后。虽余家疾患。亦未肯来视。则在他人可知也。年益老贫益甚。箪食屡空。老屋半欹。家无咫尺之僮。躬执薪水之劳。其困穷可谓极矣。而裕然自适。未尝有戚戚之意。性又和易。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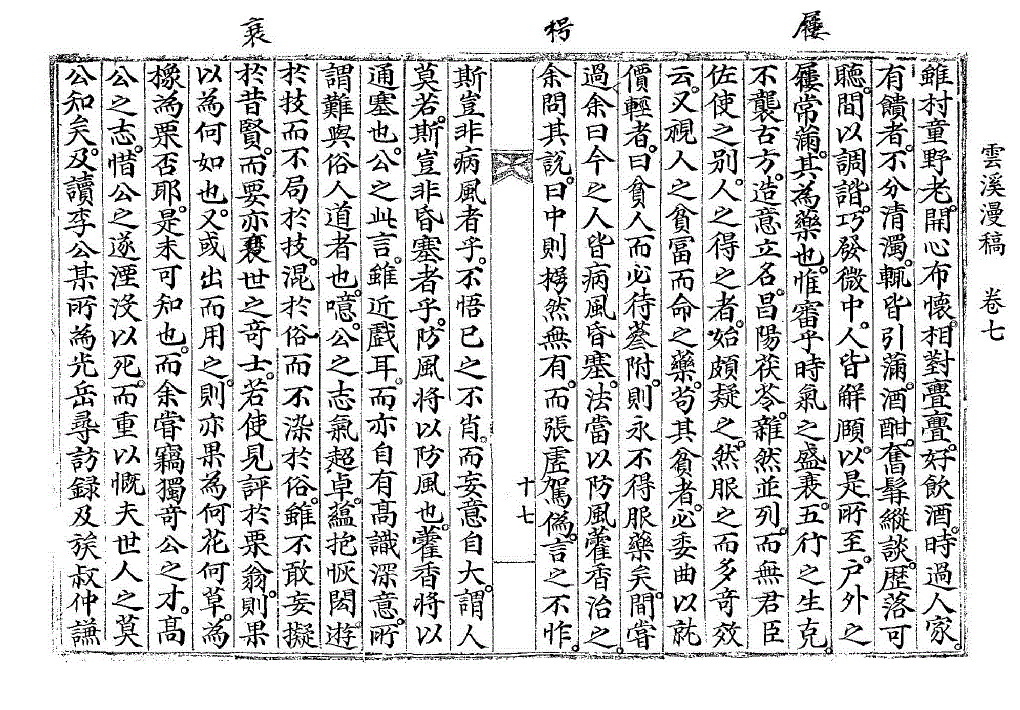 虽村童野老。开心布怀。相对亹亹。好饮酒。时过人家。有馈者。不分清浊。辄皆引满。酒酣。奋髯纵谈。历落可听。间以调谐。巧发微中。人皆解颐。以是所至。户外之屦常满。其为药也。惟审乎时气之盛衰。五行之生克。不袭古方。造意立名。昌阳茯苓。杂然并列。而无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得之者。始颇疑之。然服之而多奇效云。又视人之贫富而命之药。苟其贫者。必委曲以就价轻者。曰贫人而必待蔘附。则永不得服药矣。间尝过余曰今之人皆病风昏塞。法当以防风藿香治之。余问其说。曰中则枵然无有。而张虚驾伪。言之不怍。斯岂非病风者乎。不悟己之不肖。而妄意自大。谓人莫若。斯岂非昏塞者乎。防风将以防风也。藿香将以通塞也。公之此言。虽近戏耳。而亦自有高识深意。所谓难与俗人道者也。噫。公之志气超卓。蕴抱恢闳。游于技而不局于技。混于俗而不染于俗。虽不敢妄拟于昔贤。而要亦衰世之奇士。若使见评于栗翁。则果以为何如也。又或出而用之。则亦果为何花何草。为橡为栗否耶。是未可知也。而余尝窃独奇公之才。高公之志。惜公之遂湮没以死。而重以慨夫世人之莫公知矣。及读李公某所为光岳寻访录及族叔仲谦
虽村童野老。开心布怀。相对亹亹。好饮酒。时过人家。有馈者。不分清浊。辄皆引满。酒酣。奋髯纵谈。历落可听。间以调谐。巧发微中。人皆解颐。以是所至。户外之屦常满。其为药也。惟审乎时气之盛衰。五行之生克。不袭古方。造意立名。昌阳茯苓。杂然并列。而无君臣佐使之别。人之得之者。始颇疑之。然服之而多奇效云。又视人之贫富而命之药。苟其贫者。必委曲以就价轻者。曰贫人而必待蔘附。则永不得服药矣。间尝过余曰今之人皆病风昏塞。法当以防风藿香治之。余问其说。曰中则枵然无有。而张虚驾伪。言之不怍。斯岂非病风者乎。不悟己之不肖。而妄意自大。谓人莫若。斯岂非昏塞者乎。防风将以防风也。藿香将以通塞也。公之此言。虽近戏耳。而亦自有高识深意。所谓难与俗人道者也。噫。公之志气超卓。蕴抱恢闳。游于技而不局于技。混于俗而不染于俗。虽不敢妄拟于昔贤。而要亦衰世之奇士。若使见评于栗翁。则果以为何如也。又或出而用之。则亦果为何花何草。为橡为栗否耶。是未可知也。而余尝窃独奇公之才。高公之志。惜公之遂湮没以死。而重以慨夫世人之莫公知矣。及读李公某所为光岳寻访录及族叔仲谦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0L 页
 氏跋文。则盖皆一再见公于问药之行。而能得公最深至。不忘于既没之后。称述阐扬之不已。余于是始知世有知公者。而深幸公之庶因此而得传也。为之三复太息。辄又以平日所睹记。书其后而归之。盖非徒郑公之思。亦以感二公之意也。
氏跋文。则盖皆一再见公于问药之行。而能得公最深至。不忘于既没之后。称述阐扬之不已。余于是始知世有知公者。而深幸公之庶因此而得传也。为之三复太息。辄又以平日所睹记。书其后而归之。盖非徒郑公之思。亦以感二公之意也。先集跋
先君子所著诗文揔若干篇。呜呼此在先君子。特其绪馀耳。先君子夙负大志。以韩忠献,范文正自期待。博群籍综庶物。要为经世有用之学。一朝而加之位。则举而措之耳。当其阐大魁跻银台也。上 眷方新。朝望甚殷。若将以朝暮显庸。未几调停之说作。而义理遂晦。泾渭混流。众趋靡靡。乃先君子孑然特立。不少降其志。以格 君讨贼为急先务。再长薇垣。辄进囊封抗言。不顾触世大讳。遂以放穷溟摈下邑。嵚崎以终。而平日所蕴。竟不得尺寸施。暨乎晚年。颓然无复当世志。顾笃好朱子书。口诵心惟。兀兀穷年。服膺拳拳之意。屡形文字。盖将力赜实践。为究竟之业。且欲为之考订笺释。而年又局之。卒未有成。其为文。多积博发。下笔千言。而词理俱到。诗亦陶写性情。爱 君忧国。深得老杜风旨。然以为少技而不屑也。不规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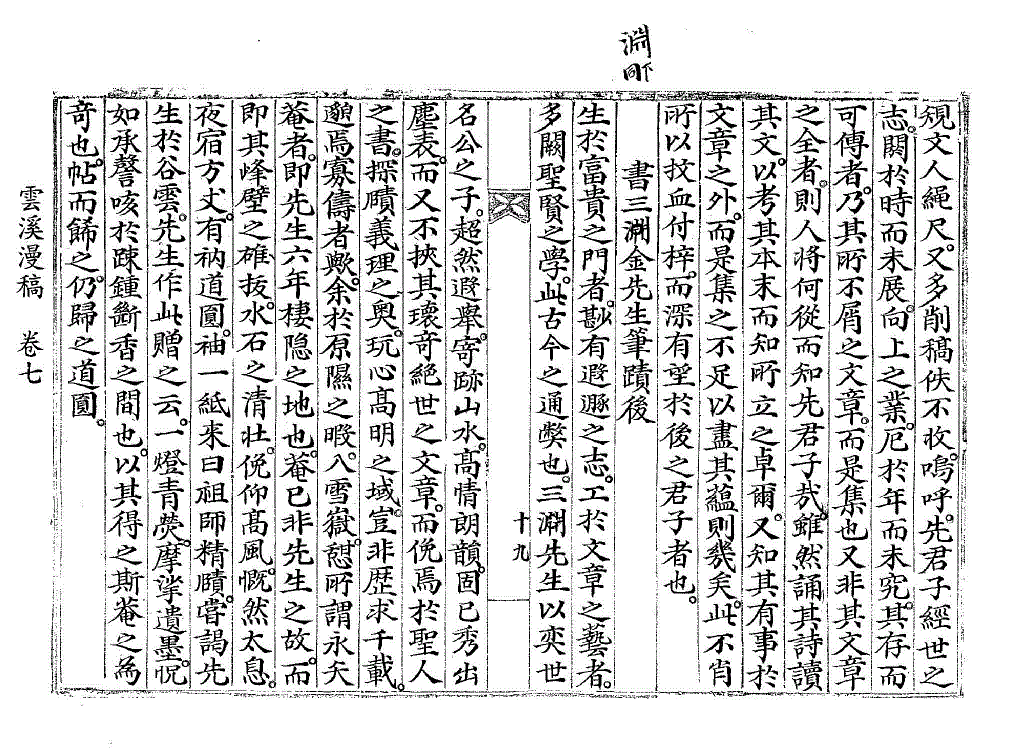 规文人绳尺。又多削稿佚不收。呜呼。先君子经世之志。阏于时而未展。向上之业。厄于年而未究。其存而可传者。乃其所不屑之文章。而是集也又非其文章之全者。则人将何从而知先君子哉。虽然诵其诗读其文。以考其本末而知所立之卓尔。又知其有事于文章之外。而是集之不足以尽其蕴则几矣。此不肖所以抆血付梓。而深有望于后之君子者也。
规文人绳尺。又多削稿佚不收。呜呼。先君子经世之志。阏于时而未展。向上之业。厄于年而未究。其存而可传者。乃其所不屑之文章。而是集也又非其文章之全者。则人将何从而知先君子哉。虽然诵其诗读其文。以考其本末而知所立之卓尔。又知其有事于文章之外。而是集之不足以尽其蕴则几矣。此不肖所以抆血付梓。而深有望于后之君子者也。书三渊金先生笔迹后
生于富贵之门者。鲜有遐遁之志。工于文章之艺者。多阙圣贤之学。此古今之通弊也。三渊先生以奕世名公之子。超然遐举。寄迹山水。高情朗韵。固已秀出尘表。而又不挟其瑰奇绝世之文章。而俛焉于圣人之书。探赜义理之奥。玩心高明之域。岂非历求千载。邈焉寡俦者欤。余于原隰之暇。入雪岳。憩所谓永矢庵者。即先生六年栖隐之地也。庵已非先生之故。而即其峰壁之雄拔。水石之清壮。俛仰高风。慨然太息。夜宿方丈。有衲道圆。袖一纸来曰祖师精赜。尝谒先生于谷云。先生作此赠之云。一灯青荧。摩挲遗墨。恍如承謦咳于疏钟断香之间也。以其得之斯庵之为奇也。帖而饰之。仍归之道圆。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1L 页
 书贾疏说与本庵族兄伯高(钟厚)氏往复书后
书贾疏说与本庵族兄伯高(钟厚)氏往复书后长子斩衰疏所谓第一子死。乃是殇死者。故不成为长子者。非愚之说。乃尤庵说也。此虽未有明据。然集考所谓生一日而死。亦名为长子者。亦岂有明白可据者耶。均之为无可据。唯其不违于礼意人情者而从之可矣。夫生一日而死。亦名为长子。则虽方生而旋死。俗所谓死胎者。亦将为长子矣。此不待经据之有无。而决知其不然矣。且传曰子生三月。父名之。死则哭之。未名则不哭也。生未名死未哭。则是不以子数之也。不以子数之。则尚安有长子之称乎。生则未名而死乃名之为长子。又从而抑其第二嫡成人者。而犹名为庶子。则揆以礼意人情。其果不违否乎。正体于上。非止指长子。即通于祖祢以上者也。今以此义推而上之。若祖若祢。本自嫡嫡相承者。而乃以其有生一日及方生而死者。遽断以祖庶祢庶。则揆以礼意人情。亦果不违否乎。子之不当庶而庶之。固失之。而祖祢之不当庶而庶之。其失尤何如也。是故必以成人为断。第一子成人而死者。为长子而服斩衰。其次嫡为庶子。未成人而死者。不得为长子而服殇服。其次嫡为长子然后。于上于下。俱无窒碍。礼意人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2H 页
 情。庶为允惬。贾氏之意盖如此。而特下语不详。以滋后人之惑耳。但有其兄而名长子。名义不顺。诚亦有如集考说者。然尤庵曰凡所谓长子。皆以成人而言。若在殇年则不得为长子。故家礼无斩衰之殇。又曰仪礼疏。不曰长子死。而必曰第一子死。可知云。盖殇死者不成为长子。稽之礼书。虽无其文。而其义则可推而知也。若集考说。则推说不去。如上所论。今从尤庵说。亦犹寡过也夫。
情。庶为允惬。贾氏之意盖如此。而特下语不详。以滋后人之惑耳。但有其兄而名长子。名义不顺。诚亦有如集考说者。然尤庵曰凡所谓长子。皆以成人而言。若在殇年则不得为长子。故家礼无斩衰之殇。又曰仪礼疏。不曰长子死。而必曰第一子死。可知云。盖殇死者不成为长子。稽之礼书。虽无其文。而其义则可推而知也。若集考说。则推说不去。如上所论。今从尤庵说。亦犹寡过也夫。追考朱子年谱。先生以继曾祖之嫡。为长子斩衰。政合于贾疏四种说。而又见先生所撰祝孺人圹记。曰生男三。伯仲皆夭。某其季也。若以集考说律之。则其伯即长子。而先生即庶子也。何以得为长子斩乎。然而先生犹为长子斩。则是先生以长子自居也。政又合于贾疏所谓第一子死。立第二嫡子。亦名长子者矣。藉使先生之为。与疏说不同。后之人以先生为据足矣。况揆诸疏说。而若是吻合者乎。不待后圣而论已定矣。益知尤庵之说。为合礼意。而集考说之得失。有不特辨矣。
中庸记疑跋주-D001
始余之读中庸也。若将有得焉而为是录矣。既而愈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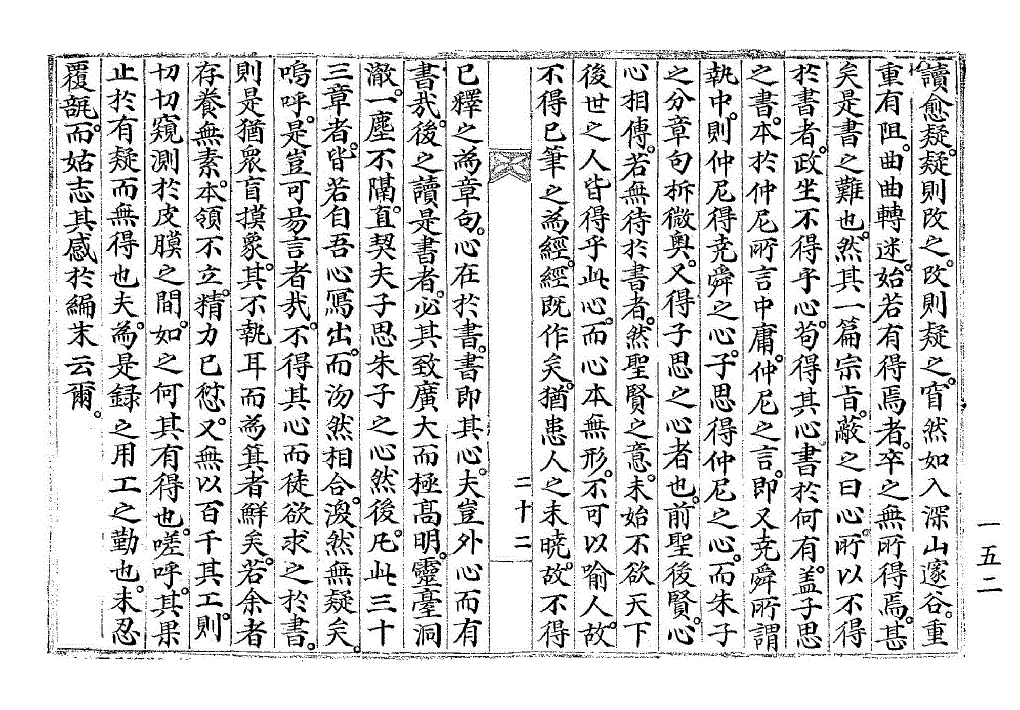 读愈疑。疑则改之。改则疑之。窅然如入深山邃谷。重重有阻。曲曲转迷。始若有得焉者。卒之无所得焉。甚矣是书之难也。然其一篇宗旨。蔽之曰心。所以不得于书者。政坐不得乎心。苟得其心。书于何有。盖子思之书。本于仲尼所言中庸。仲尼之言。即又尧舜所谓执中。则仲尼得尧舜之心。子思得仲尼之心。而朱子之分章句析微奥。又得子思之心者也。前圣后贤。心心相传。若无待于书者。然圣贤之意。未始不欲天下后世之人皆得乎此心。而心本无形。不可以喻人。故不得已笔之为经。经既作矣。犹患人之未晓。故不得已释之为章句。心在于书。书即其心。夫岂外心而有书哉。后之读是书者。必其致广大而极高明。灵台洞澈。一尘不隔。直契夫子思朱子之心然后。凡此三十三章者。皆若自吾心写出。而吻然相合。涣然无疑矣。呜呼。是岂可易言者哉。不得其心而徒欲求之于书。则是犹众盲摸象。其不执耳而为箕者鲜矣。若余者存养无素。本领不立。精力已愆。又无以百千其工。则切切窥测于皮膜之间。如之何其有得也。嗟呼。其果止于有疑而无得也夫。为是录之用工之勤也。未忍覆瓿。而姑志其感于编末云尔。
读愈疑。疑则改之。改则疑之。窅然如入深山邃谷。重重有阻。曲曲转迷。始若有得焉者。卒之无所得焉。甚矣是书之难也。然其一篇宗旨。蔽之曰心。所以不得于书者。政坐不得乎心。苟得其心。书于何有。盖子思之书。本于仲尼所言中庸。仲尼之言。即又尧舜所谓执中。则仲尼得尧舜之心。子思得仲尼之心。而朱子之分章句析微奥。又得子思之心者也。前圣后贤。心心相传。若无待于书者。然圣贤之意。未始不欲天下后世之人皆得乎此心。而心本无形。不可以喻人。故不得已笔之为经。经既作矣。犹患人之未晓。故不得已释之为章句。心在于书。书即其心。夫岂外心而有书哉。后之读是书者。必其致广大而极高明。灵台洞澈。一尘不隔。直契夫子思朱子之心然后。凡此三十三章者。皆若自吾心写出。而吻然相合。涣然无疑矣。呜呼。是岂可易言者哉。不得其心而徒欲求之于书。则是犹众盲摸象。其不执耳而为箕者鲜矣。若余者存养无素。本领不立。精力已愆。又无以百千其工。则切切窥测于皮膜之间。如之何其有得也。嗟呼。其果止于有疑而无得也夫。为是录之用工之勤也。未忍覆瓿。而姑志其感于编末云尔。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3H 页
 英宗大王御笔帖跋
英宗大王御笔帖跋我 英宗大王御笔二卷。其刊本。 当宁初服。匪颁诸臣而幸获与焉者也。其真本。即在昔年。因职事而面受 赐者也。呜呼。臣愚无知。固无以测天地之大。揆日月之明。第窃观 临御五纪之间。天人和应。民物阜殖。八域宁谧而惠泽浃于穷闾。大化巍荡而反侧归于皇极。洎 末年违豫。亟断代听之举。 离明继照。阴沴自消。转移俄顷之间。而措国势于泰山之安。 升遐之日。若臣若庶。无大无小。以至深山穷谷。耘妇牧竖。未有不奔走号哭。如丧考妣者也。抑臣之私恸。别有在焉。草芥贱微。初无葭莩之托蟠木之容。而徒荷 特达之知。扬清华历内外。以及乎崇显。秋毫皆 圣恩也。顾未有铢寸之劳。少酬夫乾坤之洪造。及至 宾天之后。猥膺敦匠之任。而不幸遭私艰。亦未竟自致于终事。含恤穷天。无地自泄。惟有 云汉之章。辉映日月。 前席亲承。恍如隔晨。未死之前。永言瞻依。推 心画以究 圣人之旨意。攀 手泽以识微臣之荣遇。庸寓其于戏不忘之思而已。昔周公升歌清庙。在庙中者。愀然如复见文王。夫清庙之歌。祗是象德之声诗。而犹感人若是。况今 圣神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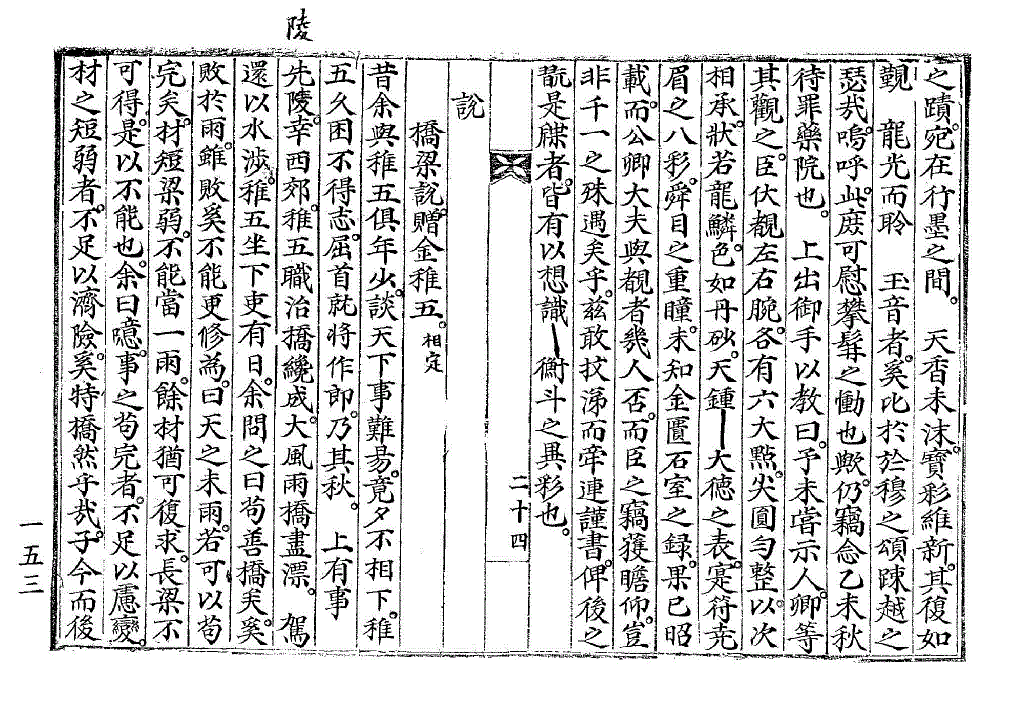 之迹。宛在行墨之间。 天香未沫。宝彩维新。其复如觐 龙光而聆 玉音者。奚比于于穆之颂疏越之瑟哉。呜呼。此庶可慰攀髯之恸也欤。仍窃念乙未秋待罪药院也。 上出御手以教曰。予未尝示人。卿等其观之。臣伏睹左右腕。各有六大点。尖圆匀整。以次相承。状若龙鳞。色如丹砂。天钟大德之表。寔符尧眉之八彩。舜目之重瞳。未知金匮石室之录。果已昭载。而公卿大夫与睹者几人否。而臣之窃获瞻仰。岂非千一之殊遇矣乎。玆敢抆涕而牵连谨书。俾后之玩是牒者。皆有以想识衡斗之异彩也。
之迹。宛在行墨之间。 天香未沫。宝彩维新。其复如觐 龙光而聆 玉音者。奚比于于穆之颂疏越之瑟哉。呜呼。此庶可慰攀髯之恸也欤。仍窃念乙未秋待罪药院也。 上出御手以教曰。予未尝示人。卿等其观之。臣伏睹左右腕。各有六大点。尖圆匀整。以次相承。状若龙鳞。色如丹砂。天钟大德之表。寔符尧眉之八彩。舜目之重瞳。未知金匮石室之录。果已昭载。而公卿大夫与睹者几人否。而臣之窃获瞻仰。岂非千一之殊遇矣乎。玆敢抆涕而牵连谨书。俾后之玩是牒者。皆有以想识衡斗之异彩也。云溪漫稿卷之七
说
桥梁说。赠金稚五(相定)。
昔余与稚五俱年少。谈天下事难易。竟夕不相下。稚五久困不得志。屈首就将作郎。乃其秋。 上有事 先陵。幸西郊。稚五职治桥才成。大风雨桥尽漂。 驾还以水涉。稚五坐下吏有日。余问之曰苟善桥矣。奚败于雨。虽败奚不能更修为。曰天之未雨。若可以苟完矣。材短梁弱。不能当一雨。馀材犹可复求。长梁不可得。是以不能也。余曰噫。事之苟完者。不足以虑变。材之短弱者。不足以济险。奚特桥然乎哉。子今而后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4H 页
 庶可知天下事之难易矣。夫时世者无津之水也。事功者利涉之桥也。事变者风雨也。人才之大小者。材与梁之别也。方宴安无事之时。势利之相求。声臭之相寻。麋至而猬集。瓦合而沙聚。詑意气则层云失其高。结交契则金兰失其利。一朝事变。猝发于意虑之外。则靡然而散。
庶可知天下事之难易矣。夫时世者无津之水也。事功者利涉之桥也。事变者风雨也。人才之大小者。材与梁之别也。方宴安无事之时。势利之相求。声臭之相寻。麋至而猬集。瓦合而沙聚。詑意气则层云失其高。结交契则金兰失其利。一朝事变。猝发于意虑之外。则靡然而散。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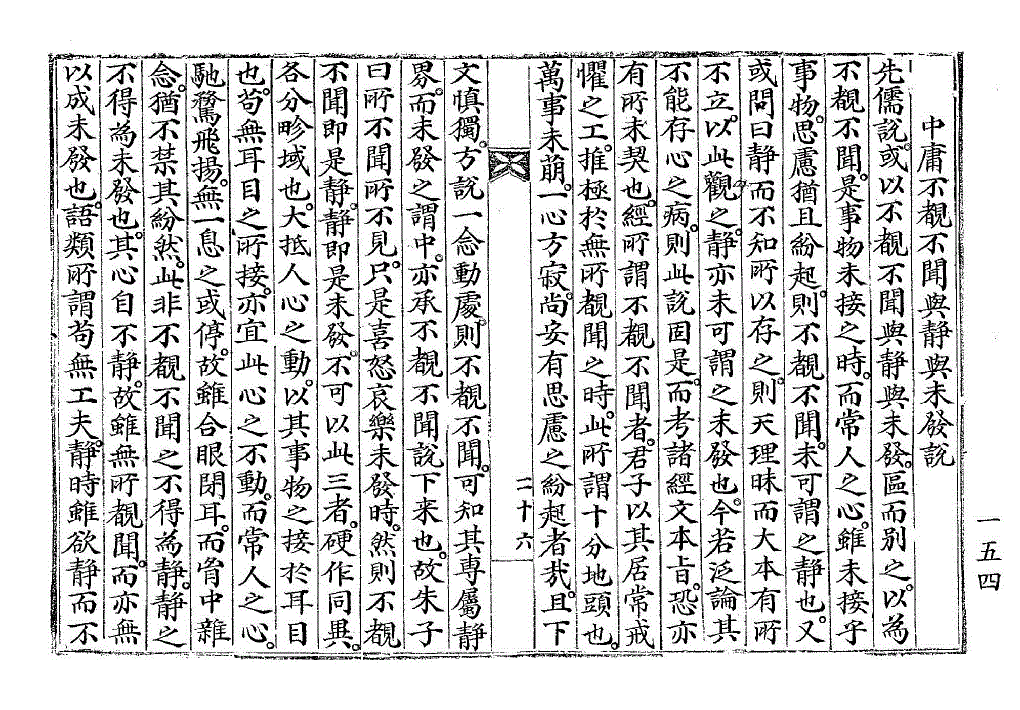 中庸不睹不闻与静与未发说
中庸不睹不闻与静与未发说先儒说。或以不睹不闻与静与未发。区而别之。以为不睹不闻。是事物未接之时。而常人之心。虽未接乎事物。思虑犹且纷起。则不睹不闻。未可谓之静也。又或问曰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则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以此观之。静亦未可谓之未发也。今若泛论其不能存心之病。则此说固是。而考诸经文本旨。恐亦有所未契也。经所谓不睹不闻者。君子以其居常戒惧之工。推极于无所睹闻之时。此所谓十分地头也。万事未萌。一心方寂。尚安有思虑之纷起者哉。且下文慎独。方说一念动处。则不睹不闻。可知其专属静界。而未发之谓中。亦承不睹不闻说下来也。故朱子曰所不闻所不见。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然则不睹不闻即是静。静即是未发。不可以此三者。硬作同异。各分畛域也。大抵人心之动。以其事物之接于耳目也。苟无耳目之所接。亦宜此心之不动。而常人之心。驰骛飞扬。无一息之或停。故虽合眼闭耳。而胸中杂念。犹不禁其纷然。此非不睹不闻之不得为静。静之不得为未发也。其心自不静。故虽无所睹闻。而亦无以成未发也。语类所谓苟无工夫。静时虽欲静而不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5H 页
 得静者。早已说破此病。而与上或问说。亦可以相发明矣。然其欲静而不得静者。政坐乎无工夫耳。苟有工夫。则当静即静。自无此病矣。此所以中和。次于戒慎之下者也。夫中和者。性情之德。天命全体。本自如是。然除非圣人之心纯乎天理者。则本源未澄。私念相续。静不成静。而无以见其未发之体。必须表里动静。交致其功。存养深固。主宰严立然后。事应既已。方寸湛然。本体昭著。无所偏倚。此之谓未发之中。譬如影过而明镜自虚。风定而澄渊自停。即是一时光景。元无许多层节矣。夫如是。则不睹不闻与静与未发。本不是各一地头。以其用工与不用工。而自成参差耳。只当察其病而加其药。不当以此之不能。而疑彼之有异也。
得静者。早已说破此病。而与上或问说。亦可以相发明矣。然其欲静而不得静者。政坐乎无工夫耳。苟有工夫。则当静即静。自无此病矣。此所以中和。次于戒慎之下者也。夫中和者。性情之德。天命全体。本自如是。然除非圣人之心纯乎天理者。则本源未澄。私念相续。静不成静。而无以见其未发之体。必须表里动静。交致其功。存养深固。主宰严立然后。事应既已。方寸湛然。本体昭著。无所偏倚。此之谓未发之中。譬如影过而明镜自虚。风定而澄渊自停。即是一时光景。元无许多层节矣。夫如是。则不睹不闻与静与未发。本不是各一地头。以其用工与不用工。而自成参差耳。只当察其病而加其药。不当以此之不能。而疑彼之有异也。性说(上)
性者生之理也。形气之谓生。理在其中。即所谓性也。盖天之所以生物者。只是理与气而已。非气不能生。非理无以生。生人生物。莫非是气。是气之中。亦莫不有是理。则天之所赋。无彼此贵贱之别。而性未始不同也。理形而上者。故浑然一体。气形而下者。故棼然万殊。但形而上者。堕在于形而下者。而一体从而为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5L 页
 万殊。是故得其气之正通者。理亦正通。得其气之偏塞者。理亦偏塞。人物之生。各随其形气之殊。而性不能不异也。虽然不能无偏全通塞者。理之乘气也。未始有偏全通塞者。理之本然也。不杂乎气而只指其理。则万殊莫非一体。而众生之性。即是天赋之性也。亦何尝有异哉。从古圣贤言性。或有以为同者。或有以为异者。特其所主而言者不同故耳。子思所谓天命之性。主天赋而言也。故朱子释之曰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言人物之性之同也。孟子所谓犬牛人三性。主人物而言也。故朱子释之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言人物之性之异也。当时门人。已不能无疑于同异之辨。而朱子晓之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其所以剖析开示者。直是金秤称出。十分分晓。而后之学者。犹不免听莹何哉。盖尝论之。上天之命。流行不息。万物生生而一理均赋。故与人只这般。与物只这般。大亦全体。小亦全体。即所谓万物之一原。而其所同者。固不得而异也。及其人物之生。气殊质异。而理在其中者。亦随而不同。于是乎人之性异于牛之性。牛之性
万殊。是故得其气之正通者。理亦正通。得其气之偏塞者。理亦偏塞。人物之生。各随其形气之殊。而性不能不异也。虽然不能无偏全通塞者。理之乘气也。未始有偏全通塞者。理之本然也。不杂乎气而只指其理。则万殊莫非一体。而众生之性。即是天赋之性也。亦何尝有异哉。从古圣贤言性。或有以为同者。或有以为异者。特其所主而言者不同故耳。子思所谓天命之性。主天赋而言也。故朱子释之曰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此言人物之性之同也。孟子所谓犬牛人三性。主人物而言也。故朱子释之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言人物之性之异也。当时门人。已不能无疑于同异之辨。而朱子晓之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其所以剖析开示者。直是金秤称出。十分分晓。而后之学者。犹不免听莹何哉。盖尝论之。上天之命。流行不息。万物生生而一理均赋。故与人只这般。与物只这般。大亦全体。小亦全体。即所谓万物之一原。而其所同者。固不得而异也。及其人物之生。气殊质异。而理在其中者。亦随而不同。于是乎人之性异于牛之性。牛之性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6H 页
 异于犬之性。物物各殊。不能相通。即所谓万物之异体。而其所异者。亦不得而同也。故自天命而言之。则性只一般。自人物而言之。则性有万品。思孟之训之不同。职由于此。而参两训而会通之。则亦可见其互相经纬者矣。盖不言一原。则无以见万物之大本。不言异体。则无以见万物之各殊。而异体之理。虽各不同。一原之赋。亦无不在。请又以程朱子江水隙日之喻申之。今夫江之水一也。其酌而取之者。或以方器。或以圆器。或以洁器。或以污器。观乎在器之水。则诚各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皆器之故。不以其器。而只论其水。则本是一江之水。岂有方圆污洁之异哉。今夫日之光一也。其隙之所受者。或有长者。或有短者。或有斜者。或有直者。观其照隙之光。则诚各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皆隙之故。不以其隙。而只论其光。则本是一日之光。岂有长短斜直之异哉。性之于人物也亦然。天命大本者。江水日光也。各随其气而偏全通塞之不同者。器之水隙之日也。不以其气。而言其理之本然。则偏者即是全者。塞者即是通者。了无彼此同异之别。又是不器不隙。而本一水与日者也。故朱子曰同中识其异。异中见其同。又曰性同气异四
异于犬之性。物物各殊。不能相通。即所谓万物之异体。而其所异者。亦不得而同也。故自天命而言之。则性只一般。自人物而言之。则性有万品。思孟之训之不同。职由于此。而参两训而会通之。则亦可见其互相经纬者矣。盖不言一原。则无以见万物之大本。不言异体。则无以见万物之各殊。而异体之理。虽各不同。一原之赋。亦无不在。请又以程朱子江水隙日之喻申之。今夫江之水一也。其酌而取之者。或以方器。或以圆器。或以洁器。或以污器。观乎在器之水。则诚各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皆器之故。不以其器。而只论其水。则本是一江之水。岂有方圆污洁之异哉。今夫日之光一也。其隙之所受者。或有长者。或有短者。或有斜者。或有直者。观其照隙之光。则诚各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皆隙之故。不以其隙。而只论其光。则本是一日之光。岂有长短斜直之异哉。性之于人物也亦然。天命大本者。江水日光也。各随其气而偏全通塞之不同者。器之水隙之日也。不以其气。而言其理之本然。则偏者即是全者。塞者即是通者。了无彼此同异之别。又是不器不隙。而本一水与日者也。故朱子曰同中识其异。异中见其同。又曰性同气异四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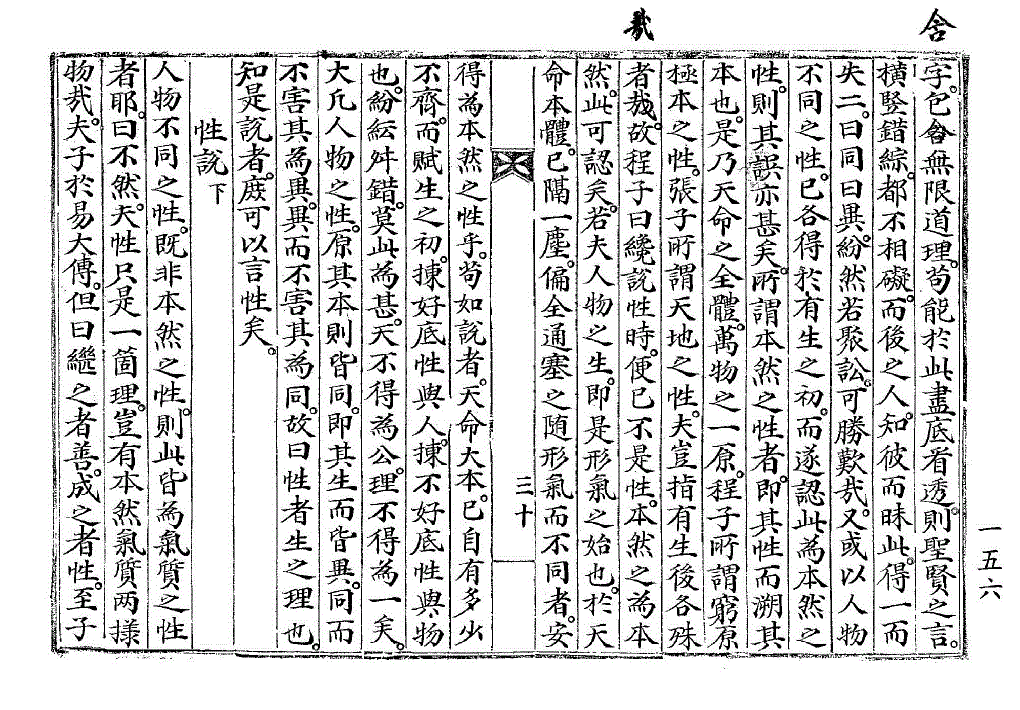 字。包含无限道理。苟能于此尽底看透。则圣贤之言。横竖错综。都不相碍。而后之人。知彼而昧此。得一而失二。曰同曰异。纷然若聚讼。可胜叹哉。又或以人物不同之性。已各得于有生之初。而遂认此为本然之性。则其误亦甚矣。所谓本然之性者。即其性而溯其本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万物之一原。程子所谓穷原极本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夫岂指有生后各殊者哉。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本然之为本然。此可认矣。若夫人物之生。即是形气之始也。于天命本体。已隔一尘。偏全通塞之随形气而不同者。安得为本然之性乎。苟如说者。天命大本。已自有多少不齐。而赋生之初。拣好底性与人。拣不好底性与物也。纷纭舛错。莫此为甚。天不得为公。理不得为一矣。大凡人物之性。原其本则皆同。即其生而皆异。同而不害其为异。异而不害其为同。故曰性者生之理也。知是说者。庶可以言性矣。
字。包含无限道理。苟能于此尽底看透。则圣贤之言。横竖错综。都不相碍。而后之人。知彼而昧此。得一而失二。曰同曰异。纷然若聚讼。可胜叹哉。又或以人物不同之性。已各得于有生之初。而遂认此为本然之性。则其误亦甚矣。所谓本然之性者。即其性而溯其本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万物之一原。程子所谓穷原极本之性。张子所谓天地之性。夫岂指有生后各殊者哉。故程子曰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本然之为本然。此可认矣。若夫人物之生。即是形气之始也。于天命本体。已隔一尘。偏全通塞之随形气而不同者。安得为本然之性乎。苟如说者。天命大本。已自有多少不齐。而赋生之初。拣好底性与人。拣不好底性与物也。纷纭舛错。莫此为甚。天不得为公。理不得为一矣。大凡人物之性。原其本则皆同。即其生而皆异。同而不害其为异。异而不害其为同。故曰性者生之理也。知是说者。庶可以言性矣。性说(下)
人物不同之性。既非本然之性。则此皆为气质之性者耶。曰不然。夫性只是一个理。岂有本然气质两㨾物哉。夫子于易大传。但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至子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7H 页
 思孟子论性愈详。而皆未有本然气质之说。诚以一性字。已尽之也。第后之人。认气为性。如荀杨韩子曰恶曰混善恶三品之说。纷然而作。故程子始拈出气质之性。以明其性无不善。而其有善恶之异者。气禀然也。又论人物之性。以为万物皆完此理。但其气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朱子因是而益阐明之然后。本然气质。较然可辨。而性之为性。始有以安顿矣。(朱子以荀杨诸子。为由于安顿性字不得。)盖人物之性。同出于天。而各载于气质。故溯言其出于天者曰本然之性。兼言其载于气者曰气质之性。以本然则人与物。元无差别。以气质则人人物物。亦各不同。诸子之论性。徒知其不同。而不知其所以不同。又不知不同之中。自有同者。故程朱子特言理与气之分。以晰其同异。而其性之体。固自如也。非析其性而两之也。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而后之人。执其名而昧其实。以本然气质。判作两㨾性。其于人物同异之际。或以所禀之理不同。而认为本然之性。或以由其气之各殊。而认为气质之性。东西角分。左右互斥。而迄未能有定矣。夫人物之性。皆禀乎一理。而所以有不同者。政以气质之或偏或正。不是天命之一彼
思孟子论性愈详。而皆未有本然气质之说。诚以一性字。已尽之也。第后之人。认气为性。如荀杨韩子曰恶曰混善恶三品之说。纷然而作。故程子始拈出气质之性。以明其性无不善。而其有善恶之异者。气禀然也。又论人物之性。以为万物皆完此理。但其气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朱子因是而益阐明之然后。本然气质。较然可辨。而性之为性。始有以安顿矣。(朱子以荀杨诸子。为由于安顿性字不得。)盖人物之性。同出于天。而各载于气质。故溯言其出于天者曰本然之性。兼言其载于气者曰气质之性。以本然则人与物。元无差别。以气质则人人物物。亦各不同。诸子之论性。徒知其不同。而不知其所以不同。又不知不同之中。自有同者。故程朱子特言理与气之分。以晰其同异。而其性之体。固自如也。非析其性而两之也。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然而后之人。执其名而昧其实。以本然气质。判作两㨾性。其于人物同异之际。或以所禀之理不同。而认为本然之性。或以由其气之各殊。而认为气质之性。东西角分。左右互斥。而迄未能有定矣。夫人物之性。皆禀乎一理。而所以有不同者。政以气质之或偏或正。不是天命之一彼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7L 页
 一此。何可以此为本然之性也。是殆见异体之理不同。而不知一原之无异也。人物之性。虽由于其气之各殊。既因其各殊之气。自成一物之性。则不论其气。而其理已各不同。何可以此为气质之性也。是殆见一原之理无异。而不知异体之不同也。然则非本然非气质。而性果何物耶。曰人物之所各得以生之理也。即所谓成之者性。而本然气质。自在其中矣。盖此一个浑然之理。人得之而为人。物得之而为物。所得以为人为物者。乃其性之当体。而本然者即其性而溯其源者也。气质者以其性而兼乎气者也。是以举此性。则本然气质。固已该之。而不可以析其一而蔽其性也。彼两说者。皆把此性当体。抛却笆篱。劳劳然上捞下摸。惟本然气质之是辨。而其谓本然者非本然也。其谓气质者非气质也。譬如论人。不识其形体之本无不具。而或以跛眇残疾。同谓之天质。不分其容貌之各自不同。而或以运动作用。替当其真面。则其为说虽殊。不知人则一也。虽然以为气质之性者。犹不失为万物之一原。以为本然之性者。却不免于大本之多端。其误尤有甚焉。或又为本然之上。又有本然之说。欲以救解其失。然本然气质。与所谓体用
一此。何可以此为本然之性也。是殆见异体之理不同。而不知一原之无异也。人物之性。虽由于其气之各殊。既因其各殊之气。自成一物之性。则不论其气。而其理已各不同。何可以此为气质之性也。是殆见一原之理无异。而不知异体之不同也。然则非本然非气质。而性果何物耶。曰人物之所各得以生之理也。即所谓成之者性。而本然气质。自在其中矣。盖此一个浑然之理。人得之而为人。物得之而为物。所得以为人为物者。乃其性之当体。而本然者即其性而溯其源者也。气质者以其性而兼乎气者也。是以举此性。则本然气质。固已该之。而不可以析其一而蔽其性也。彼两说者。皆把此性当体。抛却笆篱。劳劳然上捞下摸。惟本然气质之是辨。而其谓本然者非本然也。其谓气质者非气质也。譬如论人。不识其形体之本无不具。而或以跛眇残疾。同谓之天质。不分其容貌之各自不同。而或以运动作用。替当其真面。则其为说虽殊。不知人则一也。虽然以为气质之性者。犹不失为万物之一原。以为本然之性者。却不免于大本之多端。其误尤有甚焉。或又为本然之上。又有本然之说。欲以救解其失。然本然气质。与所谓体用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8H 页
 者不同。体用专以理言也。故体复为用。用复为体。无适而非体用矣。本然对气质而言也。今以一原之同者为本然。又以随气而不同者为本然。则理亦可以为气。气亦可以为理耶。多见其窒碍而不通也。
者不同。体用专以理言也。故体复为用。用复为体。无适而非体用矣。本然对气质而言也。今以一原之同者为本然。又以随气而不同者为本然。则理亦可以为气。气亦可以为理耶。多见其窒碍而不通也。气质说
气质之说。起于程张。至朱子论之始详。然亦未尝以气质。分属知行。陈北溪乃以为禀气清明而赋质不粹。则义理尽看得出而行为不笃。赋质纯粹而禀气不清。则所为纯正而道理全发不来。陈新安之释大学序文。亦以气清浊质粹驳。分属于知行之能不能。今以二陈之说。而稽之朱子之训。则恐皆有所不合也。夫人之生也。必禀是气而为是质焉。非于是气之外。又得了别件物事。以为之质。则岂有其气如此而其质如彼者乎。亦岂有气与质相对各发。此为知而彼为行者乎。是故大学明德章句。但曰气禀所拘。盖举气禀则质在其中矣。且于或问论气禀清浊美恶之殊。而结之曰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以此观之。则质之如此。以其气之如此。而知亦气质矣。行亦气质矣。其能知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知者。果由于或气或质而然乎哉。朱子又答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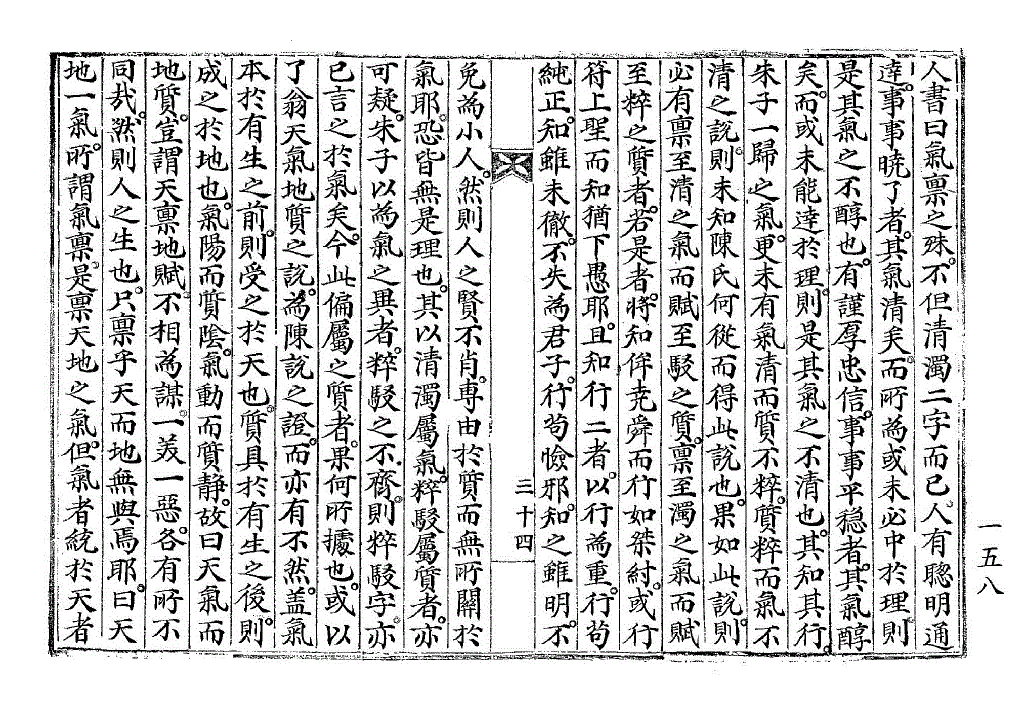 人书曰气禀之殊。不但清浊二字而已。人有聪明通达。事事晓了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或未必中于理。则是其气之不醇也。有谨厚忠信。事事平稳者。其气醇矣。而或未能达于理。则是其气之不清也。其知其行。朱子一归之气。更未有气清而质不粹。质粹而气不清之说。则未知陈氏何从而得此说也。果如此说。则必有禀至清之气而赋至驳之质。禀至浊之气而赋至粹之质者。若是者。将知侔尧舜而行如桀纣。或行符上圣而知犹下愚耶。且知行二者。以行为重。行苟纯正。知虽未彻。不失为君子。行苟憸邪。知之虽明。不免为小人。然则人之贤不肖。专由于质而无所关于气耶。恐皆无是理也。其以清浊属气。粹驳属质者。亦可疑。朱子以为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则粹驳字。亦已言之于气矣。今此偏属之质者。果何所据也。或以了翁天气地质之说。为陈说之證。而亦有不然。盖气本于有生之前。则受之于天也。质具于有生之后。则成之于地也。气阳而质阴。气动而质静。故曰天气而地质。岂谓天禀地赋。不相为谋。一美一恶。各有所不同哉。然则人之生也。只禀乎天而地无与焉耶。曰天地一气。所谓气禀。是禀天地之气。但气者统于天者
人书曰气禀之殊。不但清浊二字而已。人有聪明通达。事事晓了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或未必中于理。则是其气之不醇也。有谨厚忠信。事事平稳者。其气醇矣。而或未能达于理。则是其气之不清也。其知其行。朱子一归之气。更未有气清而质不粹。质粹而气不清之说。则未知陈氏何从而得此说也。果如此说。则必有禀至清之气而赋至驳之质。禀至浊之气而赋至粹之质者。若是者。将知侔尧舜而行如桀纣。或行符上圣而知犹下愚耶。且知行二者。以行为重。行苟纯正。知虽未彻。不失为君子。行苟憸邪。知之虽明。不免为小人。然则人之贤不肖。专由于质而无所关于气耶。恐皆无是理也。其以清浊属气。粹驳属质者。亦可疑。朱子以为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则粹驳字。亦已言之于气矣。今此偏属之质者。果何所据也。或以了翁天气地质之说。为陈说之證。而亦有不然。盖气本于有生之前。则受之于天也。质具于有生之后。则成之于地也。气阳而质阴。气动而质静。故曰天气而地质。岂谓天禀地赋。不相为谋。一美一恶。各有所不同哉。然则人之生也。只禀乎天而地无与焉耶。曰天地一气。所谓气禀。是禀天地之气。但气者统于天者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9H 页
 也。
也。情意说
为情意之说者。或云情与意发则俱发。或云先有情而后有意。甲乙相争。莫能归一。要之两说皆非是。夫心之与性。本无二体。亦非一物。未发已发。其理一也。惟其无二体。故心之发。即性之发。而情意初无二歧。非一物。故心自心性自性。而情意各有攸由。未发之前。性具于心。已发之后。情行于意。既非相对而互发。亦非此先而彼后者也。今以恻隐一端言之。乍见井孺。莫不恻隐者。固是仁之性之发。然苟无此心之知觉。亦何以发得此性乎。发之者心。而所发者性也。故当恻隐而恻隐者。性发而为情也。知恻隐而恻隐之者。心发而为意也。性无为。故情无思惟。心能觉。故意能运用。无思惟。故情之流行皆由意。能运用。故意之商量皆因情。此其所以发无二歧。而各有攸由者也。朱夫子人使舟车之喻。取譬甚明。盖舟车会行而不能自行。其使之行者人也。之南之北。或沿或溯。莫非人使之而舟车行也。人非舟车。无所使。舟车非人。无以行。人与舟车。虽非一物。而实亦相舍不得者也。若如甲者之说。则是舟车与人。互行而并驰也。如乙者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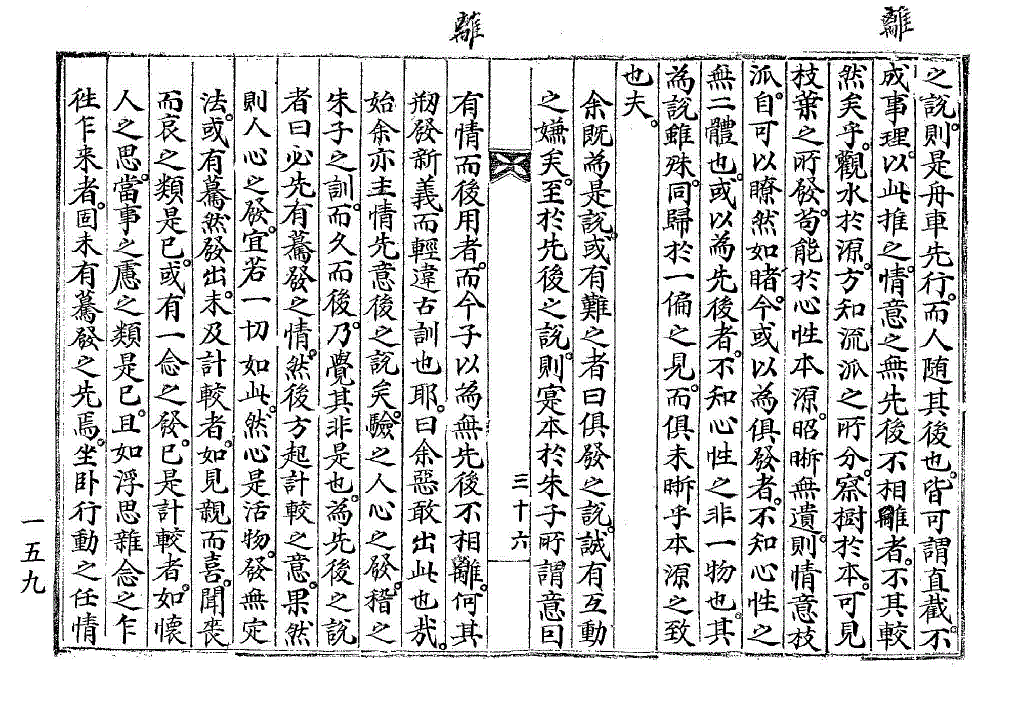 之说。则是舟车先行。而人随其后也。皆可谓直截。不成事理。以此推之。情意之无先后不相离者。不其较然矣乎。观水于源。方知流派之所分。察树于本。可见枝叶之所发。苟能于心性本源。昭晰无遗。则情意枝派。自可以瞭然如睹。今或以为俱发者。不知心性之无二体也。或以为先后者。不知心性之非一物也。其为说虽殊。同归于一偏之见。而俱未晢乎本源之致也夫。
之说。则是舟车先行。而人随其后也。皆可谓直截。不成事理。以此推之。情意之无先后不相离者。不其较然矣乎。观水于源。方知流派之所分。察树于本。可见枝叶之所发。苟能于心性本源。昭晰无遗。则情意枝派。自可以瞭然如睹。今或以为俱发者。不知心性之无二体也。或以为先后者。不知心性之非一物也。其为说虽殊。同归于一偏之见。而俱未晢乎本源之致也夫。余既为是说。或有难之者曰俱发之说。诚有互动之嫌矣。至于先后之说。则寔本于朱子所谓意因有情而后用者。而今子以为无先后不相离。何其刱发新义而轻违古训也耶。曰余恶敢出此也哉。始余亦主情先意后之说矣。验之人心之发。稽之朱子之训。而久而后。乃觉其非是也。为先后之说者曰必先有蓦发之情。然后方起计较之意。果然则人心之发。宜若一切如此。然心是活物。发无定法。或有蓦然发出。未及计较者。如见亲而喜。闻丧而哀之类是已。或有一念之发。已是计较者。如怀人之思。当事之虑之类是已。且如浮思杂念之乍往乍来者。固未有蓦发之先焉。坐卧行动之任情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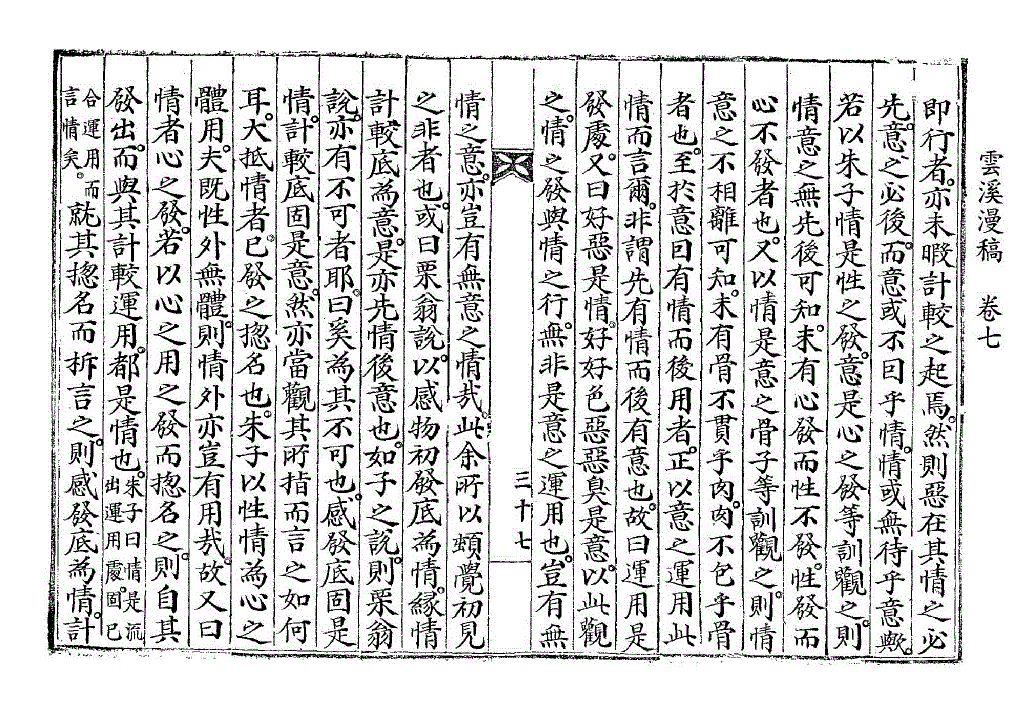 即行者。亦未暇计较之起焉。然则恶在其情之必先。意之必后。而意或不因乎情。情或无待乎意欤。若以朱子情是性之发。意是心之发等训观之。则情意之无先后可知。未有心发而性不发。性发而心不发者也。又以情是意之骨子等训观之。则情意之不相离可知。未有骨不贯乎肉。肉不包乎骨者也。至于意因有情而后用者。正以意之运用此情而言尔。非谓先有情而后有意也。故曰运用是发处。又曰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是意。以此观之。情之发与情之行。无非是意之运用也。岂有无情之意。亦岂有无意之情哉。此余所以顿觉初见之非者也。或曰栗翁说。以感物初发底为情。缘情计较底为意。是亦先情后意也。如子之说。则栗翁说。亦有不可者耶。曰奚为其不可也。感发底固是情。计较底固是意。然亦当观其所指而言之如何耳。大抵情者。已发之揔名也。朱子以性情为心之体用。夫既性外无体。则情外亦岂有用哉。故又曰情者心之发。若以心之用之发而揔名之。则自其发出。而与其计较运用。都是情也。(朱子曰情是流出运用处。固已合运用而言情矣。)就其揔名而析言之。则感发底为情。计
即行者。亦未暇计较之起焉。然则恶在其情之必先。意之必后。而意或不因乎情。情或无待乎意欤。若以朱子情是性之发。意是心之发等训观之。则情意之无先后可知。未有心发而性不发。性发而心不发者也。又以情是意之骨子等训观之。则情意之不相离可知。未有骨不贯乎肉。肉不包乎骨者也。至于意因有情而后用者。正以意之运用此情而言尔。非谓先有情而后有意也。故曰运用是发处。又曰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是意。以此观之。情之发与情之行。无非是意之运用也。岂有无情之意。亦岂有无意之情哉。此余所以顿觉初见之非者也。或曰栗翁说。以感物初发底为情。缘情计较底为意。是亦先情后意也。如子之说。则栗翁说。亦有不可者耶。曰奚为其不可也。感发底固是情。计较底固是意。然亦当观其所指而言之如何耳。大抵情者。已发之揔名也。朱子以性情为心之体用。夫既性外无体。则情外亦岂有用哉。故又曰情者心之发。若以心之用之发而揔名之。则自其发出。而与其计较运用。都是情也。(朱子曰情是流出运用处。固已合运用而言情矣。)就其揔名而析言之。则感发底为情。计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60L 页
 较底为意。又就其感发而析言之。则性之发为情。心之发为意。盖以心性而合言。则情意为一。析心性而对言。则情意为二。随其所指。各自不同。然则栗翁之说。非有可疑。而后之人。不察原委之有自。硬作先后之异发。则亦岂非栗翁所谓执言而迷指者耶。(栗翁说。正欲明其情意之无二歧。非以为发有先后也。观其上文性发为情。非无心也。心发为意。非无性也等语。则情意之发无先后。亦可知矣。)或曰子之言似矣。然大学诚意章。以意为几。通书诚几篇。以情为几。岂非情意之几。各有不同者耶。曰此亦其所主而言者不同故也。大学主乎心而言之。故以意为几。通书主乎性而言之。故以情为几。其实一几也。非有情之几。又有意之几者也。或曰情意之发。既非二几。则主意言之。亦可以混情为意也耶。曰主意而言。情亦在其中矣。然意虽运情。而不能统情。故情可以混意。意不可以混情。如计较运用。固可谓之情。而恻隐羞恶。未可谓之意也。(朱子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虽然以心而言。则性情与意。皆统于心。以其总理气该体用故也。其错综贯通之妙。有如此者。
较底为意。又就其感发而析言之。则性之发为情。心之发为意。盖以心性而合言。则情意为一。析心性而对言。则情意为二。随其所指。各自不同。然则栗翁之说。非有可疑。而后之人。不察原委之有自。硬作先后之异发。则亦岂非栗翁所谓执言而迷指者耶。(栗翁说。正欲明其情意之无二歧。非以为发有先后也。观其上文性发为情。非无心也。心发为意。非无性也等语。则情意之发无先后。亦可知矣。)或曰子之言似矣。然大学诚意章。以意为几。通书诚几篇。以情为几。岂非情意之几。各有不同者耶。曰此亦其所主而言者不同故也。大学主乎心而言之。故以意为几。通书主乎性而言之。故以情为几。其实一几也。非有情之几。又有意之几者也。或曰情意之发。既非二几。则主意言之。亦可以混情为意也耶。曰主意而言。情亦在其中矣。然意虽运情。而不能统情。故情可以混意。意不可以混情。如计较运用。固可谓之情。而恻隐羞恶。未可谓之意也。(朱子曰志与意都属情。情字较大。)虽然以心而言。则性情与意。皆统于心。以其总理气该体用故也。其错综贯通之妙。有如此者。四端七情说
夫四端主乎理。七情主乎气。虽主乎理而非无气也。
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61H 页
 虽主乎气而非无理也。特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其所发者无二歧也。语类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退溪引此。以主互发之说。以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辨之曰七情统言人心之动。四端摭出其善一边。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二先生之说。各有不同。未知何所适从。然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只发于气。则子思何以气之未发者。直谓之大本乎。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恻隐羞恶。只发于理。则孟子何以理之发者。并谓之心乎。朱子于中庸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于孟子注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以此观之。喜怒哀乐。恻隐羞恶。同是情也。而七情亦发于性。四端亦发于心。何尝有理发气发之异哉。然心之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其一而言之。则心性之发。元无二歧。而四端已包于七情之中。自其二而言之。则七情揔一心之用而主乎气。四端专五性之发而主乎理。窃恐语类所谓理之发气之发。其义盖亦如此。栗谷说。可谓深得朱子之旨。而真是四七之定案也。然而后来参差之论。
虽主乎气而非无理也。特所主而言者不同。而其所发者无二歧也。语类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退溪引此。以主互发之说。以为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栗谷辨之曰七情统言人心之动。四端摭出其善一边。四端专言理。七情兼言气。二先生之说。各有不同。未知何所适从。然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只发于气。则子思何以气之未发者。直谓之大本乎。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恻隐羞恶。只发于理。则孟子何以理之发者。并谓之心乎。朱子于中庸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于孟子注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以此观之。喜怒哀乐。恻隐羞恶。同是情也。而七情亦发于性。四端亦发于心。何尝有理发气发之异哉。然心之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其一而言之。则心性之发。元无二歧。而四端已包于七情之中。自其二而言之。则七情揔一心之用而主乎气。四端专五性之发而主乎理。窃恐语类所谓理之发气之发。其义盖亦如此。栗谷说。可谓深得朱子之旨。而真是四七之定案也。然而后来参差之论。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61L 页
 犹复多端。或以心之感物。触于理则理发。触于气则气发。而析理气为或先或后。或以恻隐羞恶本乎性命。喜怒哀乐由于形气。而判四七为道心人心。此不但未喻栗谷之意。正坐于本原上。未能透破耳。朱子曰能觉者气之灵。所觉者心之理。夫心者气之灵。而理具乎其中。能知能觉者。以其灵也。所知所觉者。即其所具乎中者也。盖不特性命之为理。一身形气。亦莫不有其理。(性命形气。同一理也。)不特形气之为气。天命全体。亦不离于是气。(方寸躯壳。同一气也。)其总宰理气。该贮发用者心也。是故事物所感。或有于理于气之殊。而此心所应。只是一个知觉而已。知觉固气之发处。而气之发。即理之发也。(理不能自发。而发之者气也。气则发之。而所发者理也。)苟无是气。何以知觉。苟无是理。何所知觉。由是观之。恶在其理气之或先或后者哉。人心道心。虽有生于气原于性之异。今以四七之目。参较论之。则四端之恻隐。即七情之爱与哀也。四端之羞恶。即七情之恶与怒也。辞让是非。亦不出于爱恶之情。然则道心也是七情。人心也是七情。且如孩提之无知也。而见其父母则喜。见人之驱其父母则怒。此果为发于形气者耶。程子曰圣人临事而惧。未尝无惧。仁民而爱物。未尝无爱。
犹复多端。或以心之感物。触于理则理发。触于气则气发。而析理气为或先或后。或以恻隐羞恶本乎性命。喜怒哀乐由于形气。而判四七为道心人心。此不但未喻栗谷之意。正坐于本原上。未能透破耳。朱子曰能觉者气之灵。所觉者心之理。夫心者气之灵。而理具乎其中。能知能觉者。以其灵也。所知所觉者。即其所具乎中者也。盖不特性命之为理。一身形气。亦莫不有其理。(性命形气。同一理也。)不特形气之为气。天命全体。亦不离于是气。(方寸躯壳。同一气也。)其总宰理气。该贮发用者心也。是故事物所感。或有于理于气之殊。而此心所应。只是一个知觉而已。知觉固气之发处。而气之发。即理之发也。(理不能自发。而发之者气也。气则发之。而所发者理也。)苟无是气。何以知觉。苟无是理。何所知觉。由是观之。恶在其理气之或先或后者哉。人心道心。虽有生于气原于性之异。今以四七之目。参较论之。则四端之恻隐。即七情之爱与哀也。四端之羞恶。即七情之恶与怒也。辞让是非。亦不出于爱恶之情。然则道心也是七情。人心也是七情。且如孩提之无知也。而见其父母则喜。见人之驱其父母则怒。此果为发于形气者耶。程子曰圣人临事而惧。未尝无惧。仁民而爱物。未尝无爱。云溪漫稿卷之七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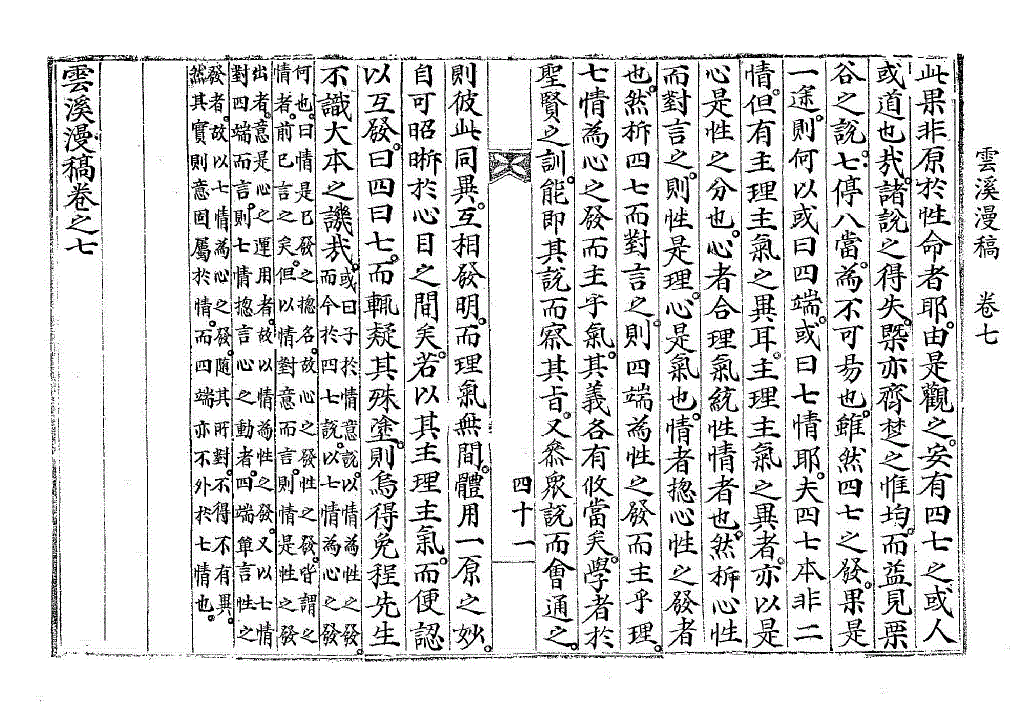 此果非原于性命者耶。由是观之。安有四七之或人或道也哉。诸说之得失。槩亦齐楚之惟均。而益见栗谷之说。七停八当。为不可易也。虽然四七之发。果是一途。则何以或曰四端。或曰七情耶。夫四七本非二情。但有主理主气之异耳。主理主气之异者。亦以是心是性之分也。心者合理气统性情者也。然析心性而对言之。则性是理。心是气也。情者揔心性之发者也。然析四七而对言之。则四端为性之发而主乎理。七情为心之发而主乎气。其义各有攸当矣。学者于圣贤之训。能即其说而察其旨。又参众说而会通之。则彼此同异。互相发明。而理气无间。体用一原之妙。自可昭晰于心目之间矣。若以其主理主气。而便认以互发。曰四曰七。而辄疑其殊涂。则乌得免程先生不识大本之讥哉。(或曰子于情意说。以情为性之发。而今于四七说。以七情为心之发何也。曰情是已发之揔名。故心之发性之发。皆谓之情者。前已言之矣。但以情对意而言。则情是性之发出者。意是心之运用者。故以情为性之发。又以七情对四端而言。则七情揔言心之动者。四端单言性之发者。故以七情为心之发。随其所对。不得不有异。然其实则意固属于情。而四端亦不外于七情也。)
此果非原于性命者耶。由是观之。安有四七之或人或道也哉。诸说之得失。槩亦齐楚之惟均。而益见栗谷之说。七停八当。为不可易也。虽然四七之发。果是一途。则何以或曰四端。或曰七情耶。夫四七本非二情。但有主理主气之异耳。主理主气之异者。亦以是心是性之分也。心者合理气统性情者也。然析心性而对言之。则性是理。心是气也。情者揔心性之发者也。然析四七而对言之。则四端为性之发而主乎理。七情为心之发而主乎气。其义各有攸当矣。学者于圣贤之训。能即其说而察其旨。又参众说而会通之。则彼此同异。互相发明。而理气无间。体用一原之妙。自可昭晰于心目之间矣。若以其主理主气。而便认以互发。曰四曰七。而辄疑其殊涂。则乌得免程先生不识大本之讥哉。(或曰子于情意说。以情为性之发。而今于四七说。以七情为心之发何也。曰情是已发之揔名。故心之发性之发。皆谓之情者。前已言之矣。但以情对意而言。则情是性之发出者。意是心之运用者。故以情为性之发。又以七情对四端而言。则七情揔言心之动者。四端单言性之发者。故以七情为心之发。随其所对。不得不有异。然其实则意固属于情。而四端亦不外于七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