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x 页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书
书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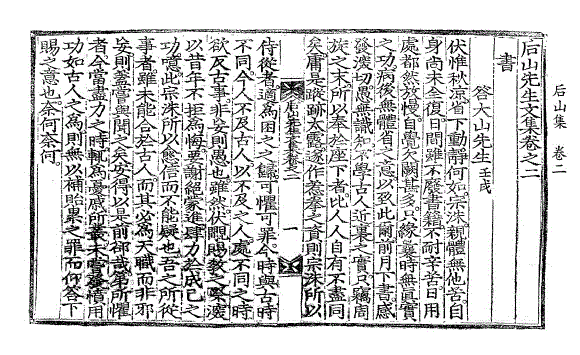 答大山先生(壬戌)
答大山先生(壬戌)伏惟秋凉。省下动静何如。宗洙。亲体无他苦。自身尚未全复。日间虽不废书籍。不耐辛苦。日用处都然放慢。自觉欠阙甚多。只缘曩时无真实之功。病后无体省之意。以致此尔。前月下书。感发深切。愚无识知。不学古人近里之实。只窃周旋之末。所以奉于座下者。比人人自有不尽同矣。庸是踪迹太露。遂作惹拳之资则宗洙所以侍从者。适为困之之归。可惧可罪。今时与古时不同。今人不及古人。以不及之人。处不同之时。欲反古事。非妄则愚也。虽然。伏覸赐教之际。深以昔年不拒为悔。要谢绝蒙进。肆力于成己之功。噫。此宗洙所以愈信而不能疑也。吾之所从事者。虽未能合于古人。而其必为天职而非邪妄。则盖尝与闻之矣。安得以是前郤哉。第所惧者。今当尽力之时。辄为忧戚所丛。未尝发愤用功如古人之为。则无以补贻累之罪而仰答下赐之意也。奈何奈何。
上先生(甲子)
振作之诲。思继今服膺从事。未知能不倍训否。窃尝谬谓发露不如沈潜。轻俊不如重缓。一向倚著此一边。不知不觉。用力慢泛。气象胶滞。卒未有分寸之进。承诲惕然。盖欲当下跃如。但未知能终始惟一耳。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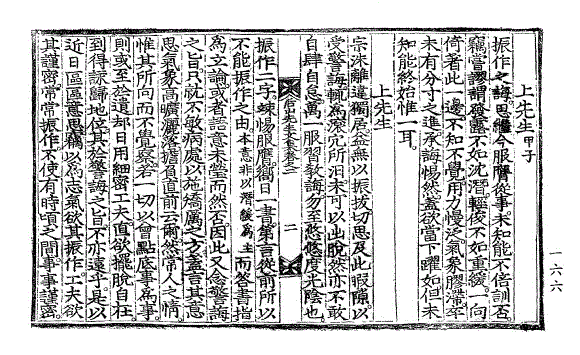 上先生
上先生宗洙离违独居。益无以振拔。切思及此暇隙。以受警诲。辄为滚冗所汩。未可以出脱。然亦不敢自肆自怠。万一服习教诲。勿至悠悠度光阴也。振作二字。竦惕服膺。向日一书。第言从前所以不能振作之由。(本意非以潜缓为主)而答书指为立论。或者语意未莹而然否。因此又念警诲之旨。只就不敏病处以施矫厉之方。盖言其意思气象高旷洒落。担负直前云尔。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觉察。若一切以曾点底事为事。则或至于遗却日用细密工夫。直欲摆脱自在。到得咏归地位。其于警诲之旨。不亦远乎。是以近日区区意思。窃以为志气欲其振作。工夫欲其谨密。常常振作。不使有时顷之间。事事谨密。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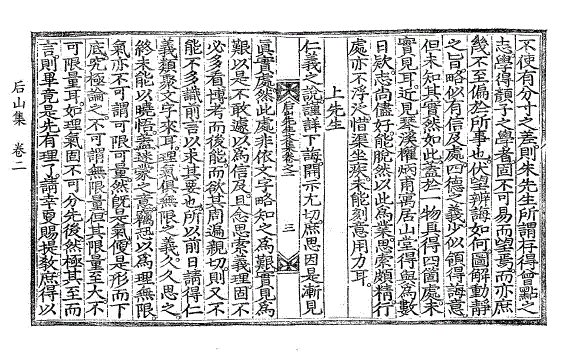 不使有分寸之差。则朱先生所谓存得曾点之志。学得颜子之学者。固不可易而望焉。而亦庶几不至偏于所事也。伏望辨诲如何。图解动静之旨。略似有信及处。四德之义。少似领得诲意。但未知其实然如此。盖于一物具得四个处。未实见耳。近见琴溪权炳甫寓居山堂得与为数日款。志尚尽好。能脱然以此为业。思索颇精。行处亦不浮泛。惜渠坐疾。未能刻意用力耳。
不使有分寸之差。则朱先生所谓存得曾点之志。学得颜子之学者。固不可易而望焉。而亦庶几不至偏于所事也。伏望辨诲如何。图解动静之旨。略似有信及处。四德之义。少似领得诲意。但未知其实然如此。盖于一物具得四个处。未实见耳。近见琴溪权炳甫寓居山堂得与为数日款。志尚尽好。能脱然以此为业。思索颇精。行处亦不浮泛。惜渠坐疾。未能刻意用力耳。上先生
仁义之说。谨详下诲。开示尤切。庶思因是渐见真实处。然此处非依文字略知之为艰。实见为艰。以是不敢遽以为信及。且念思索义理。固不必多看博考而后能。而欲其周遍亲切。则又不能不多识前言以求其要也。所以前日请得仁义类聚文字来耳。理气俱无限之义。久久思之。终未能以晓悟。盖迷蒙之意。窃恐以为理无限。气亦不可谓可限可量。然既是气。便是形而下底。究极论之。不可谓无限量。但其限量至大。不可限量耳。如理气固不可分先后。然极其至而言。则毕竟是先有理了。请幸更赐提教。庶得以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7L 页
 致思耳。竦俟竦俟。
致思耳。竦俟竦俟。答先生(丙寅)
宗洙从前见解。颇将空荡道理作活计。于精密细微处。不知觉察。冬来。渐觉靠不得焉。而未用力也。伏承下教。反己体验。操守兢惕八字。极是切当。所谓非面命之。亦提其耳。方思洗心以从事焉。但自家亦不知自家耳。因念学问之道。元来有个规模。然其间节度条目。则不容不随其所见力量而有所变。每变每有益则学不差矣。经历来。似是如此。未知近否。
答先生
前献疑义。宜多谬戾。以承颜遽。未卒闻教。伏恨。与权生问答疑义。彼时略略说及。亦未得其究竟。近更思量。其惑愈甚。不得不略成小说以质焉。伏乞有以辨诲恳望。从前见解。妄要多学。不知不觉。入杂驳中去了。心地转无靠实处。纵说操存涵养工夫。终是精神重处。在彼而不在此。为害极大。盖学问未说到反约处。只博学中煞有先后缓急之分。欲博而不得其要。则泛滥无主而归于杂而已矣。私窃自谓博学不可只说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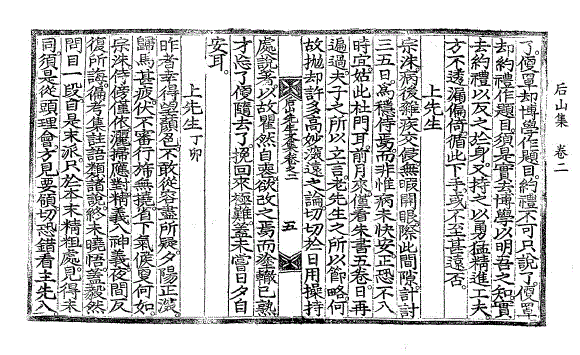 了。便罩却博学作题目。约礼不可只说了。便罩却约礼作题目。须是实去博学以明吾之知。实去约礼以反之于身。又持之以勇猛精进工夫。方不透漏偏倚。循此下手。或不至甚远否。
了。便罩却博学作题目。约礼不可只说了。便罩却约礼作题目。须是实去博学以明吾之知。实去约礼以反之于身。又持之以勇猛精进工夫。方不透漏偏倚。循此下手。或不至甚远否。上先生
宗洙。病后杂疾交侵。无暇开眼。际此间隙。计讨三五日。为稳侍焉。而非惟病未快安。正恐不入时宜。姑此杜门耳。前月来。仅看朱书五卷。日再遍过。夫子之所以立言。老先生之所以节略。何故抛却许多高妙深远之论。切切于日用操持处说著。以故瞿然自丧。欲改之焉而涂辙已熟。才忘了便随去了。挽回来极难。盖未尝日夕自安耳。
上先生(丁卯)
昨者幸得望颜色。不敢从容尽所疑。夕阳正深。归马甚疲。伏不审行旆无挠。省下气候更何如。宗洙。侍傍仅依。洒扫应对。精义入神义。夜间反复所诲。遍考集注语类诸说。终未晓悟。盖毅然问目一段。自是末派。只于本末精粗处。见得未同。须是从头理会。方见要领。切恐错看主先入。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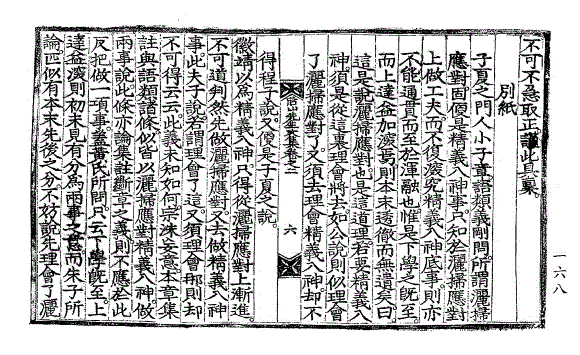 不可不急取正。谨此具禀。
不可不急取正。谨此具禀。别纸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语类义刚问。所谓洒扫应对。固便是精义入神事。只知于洒扫应对上做工夫。而不复深究精义入神底事。则亦不能通贯而至于浑融也。惟是下学之既至。而上达益加深焉。则本末透彻而无遗矣。曰。这是说洒扫应对。也是这道理。若要精义入神。须是从这里理会将去。如公说则似理会了洒扫应对了。又须去理会精义入神。却不得程子说。又便是子夏之说。
徽靖以为精义入神。只得从洒扫应对上渐进。不可道判然先做洒扫应对。又去做精义入神事。此夫子说。若谓理会了这。又须理会那则却不可得云云。此义未知如何。宗洙妄意。本章集注与语类诸条。似皆以洒扫应对精义入神。做两事说。此条亦论集注断章之义。则不应于此反把做一项事。盖黄氏所问。只云下学既至。上达益深则初未见有分为两事之意。而朱子所论。匹似有本末先后之分。不妨说先理会了洒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9H 页
 扫应对了。又须是去理会精义入神底事。未知如何。(此义只于却不得三字上分破。一是问者。一是答者之辞。)大抵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虽则有大小远近之不同。而自是其然之事。似不可以下学上达言之。朱子亦多以为言。未知与子夏本意有不同否。伏乞批诲。
扫应对了。又须是去理会精义入神底事。未知如何。(此义只于却不得三字上分破。一是问者。一是答者之辞。)大抵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虽则有大小远近之不同。而自是其然之事。似不可以下学上达言之。朱子亦多以为言。未知与子夏本意有不同否。伏乞批诲。上先生
常以十里为远。况岭洛千里之路。安得收寒暄之详耶。秋序忽晚。伏未审旅中气候何如。坌纠之地。非素心所安乐者。日夕慕仰区区之至。宗洙。自离教诲。不敢不小心。然独居之久。渐觉无进益。前日师靖兄。寓书致告奋厉之教。承闻瞿然。思有以直下起发。亦未能也。中庸更读过。别无大疑晦大解悟。觉是蟠天际地。无外无内底物事。天然自在。逼塞充满。只是自家动目举足。便凿坏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紧切下手处。不敢放其四体。不敢大其声气。以夫操存之旨。为日间警省之资。庶几异日拜侍。有以点其是非也。刊补。随疑义检看。间有数四傍照处。小子所见诸说。似极精微不可易。密庵先生万一或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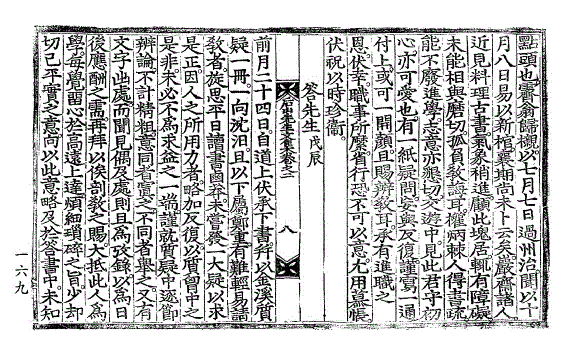 点头也。霁翁归榇。以七月七日过州治。闻以十月八日易以新棺。襄期尚未卜云矣。岩斋诸人。近见料理古书。气象稍进。顾此块居。辄有障碍。未能相与磨切。孤负教诲耳。权炳棘人得书疏。能不废进学。志意亦恳切。交游中。见此君守初心。亦可爱也。有一纸疑问。妄与反复。谨写一通付上。或可一开颜。且赐辨教耳。承有进职之 恩。伏幸。职事所縻。省行恐不可以意。尤用慕怅。伏祝以时珍卫。
点头也。霁翁归榇。以七月七日过州治。闻以十月八日易以新棺。襄期尚未卜云矣。岩斋诸人。近见料理古书。气象稍进。顾此块居。辄有障碍。未能相与磨切。孤负教诲耳。权炳棘人得书疏。能不废进学。志意亦恳切。交游中。见此君守初心。亦可爱也。有一纸疑问。妄与反复。谨写一通付上。或可一开颜。且赐辨教耳。承有进职之 恩。伏幸。职事所縻。省行恐不可以意。尤用慕怅。伏祝以时珍卫。答先生(戊辰)
前月二十四日。自道上伏承下书。并以金溪质疑一册。一向沈汩。且以下属郑重。有难轻易请教者。旋思平日读书卤莽。未尝发一大疑以求是正。因人之所用力者。略加反复。以质胸中之是非。未必不为求益之一端。谨就质疑中逐节辨论。不计精粗。意同者寘之。不同者举之。又有文字出处。而闻见偶及处则且为考录。以为日后应酬之需。再拜以俟剖教之赐。大抵此人为学。每觉留心于高远上达。烦细琐碎之旨。少却切己平实之意。向以此意略及于答书中。未知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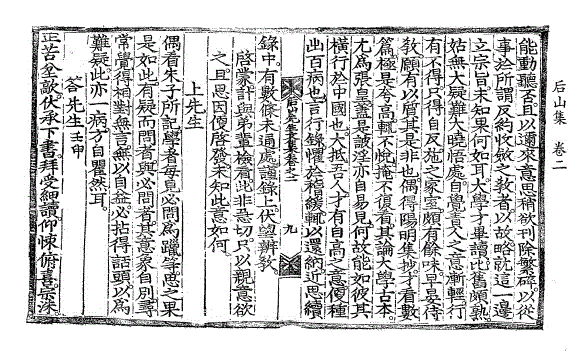 能动听否。且以迩来意思稍欲刊除繁碎。以从事于所谓反约收敛之教者。以故。略就这一边立宗旨。未知果何如耳。大学才毕读。比旧颇熟。姑无大疑难大晓悟处。自觉责人之意渐轻。行有不得。只得自反。施之家室。颇有馀味。早晏侍教。愿有以质其是非也。偶得阳明集抄。才看数篇。极是夸高。辄不悦。掩不复看。其论大学古本。尤为张皇。盖是诐淫亦自易见。何故能如彼其横行于中国也。大抵吾人。才有自高之意。便种出百病也。言行录。惧于稽缓。辄以还纳。近思续录中。有数条未通处。谨录上。伏望辨教。
能动听否。且以迩来意思稍欲刊除繁碎。以从事于所谓反约收敛之教者。以故。略就这一边立宗旨。未知果何如耳。大学才毕读。比旧颇熟。姑无大疑难大晓悟处。自觉责人之意渐轻。行有不得。只得自反。施之家室。颇有馀味。早晏侍教。愿有以质其是非也。偶得阳明集抄。才看数篇。极是夸高。辄不悦。掩不复看。其论大学古本。尤为张皇。盖是诐淫亦自易见。何故能如彼其横行于中国也。大抵吾人。才有自高之意。便种出百病也。言行录。惧于稽缓。辄以还纳。近思续录中。有数条未通处。谨录上。伏望辨教。启蒙。计与弟辈检看。此非急切。只以亲意欲之。且思因便启发。未知此意如何。
上先生
偶看朱子所记。学者每见必问为躐等。思之果是如此。有疑而问者。与必问者。其意象自别。寻常觉得相对无言。无以自益。必拈得话头。以为难疑。此亦一病。方自瞿然耳。
答先生(壬申)
正苦坌歊。伏承下书。拜受细读。仰悚俯喜。宗洙。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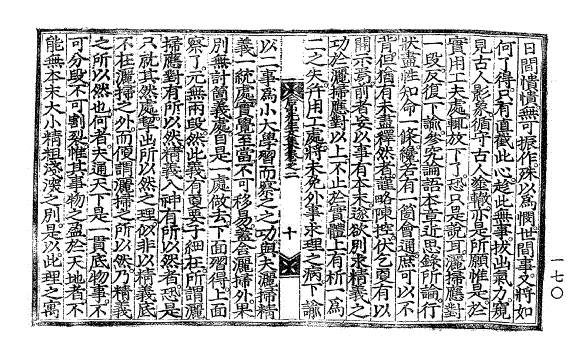 日间愦愦。无可振作。殊以为悯。世间事。又将如何了得。只有直截此心。趁此无事。拔出气力。窥见古人影象。循守古人涂辙。亦是所愿惟是。于实用工夫处。辄放下了。恐只是说耳。洒扫应对一段。反复下谕。参究论语本章近思录所论。行状尽性知命一条。才若有一个会通。庶可以不背。但犹有未尽释然者。谨略陈控。伏乞更有以开示焉。前者妄以事有本末。遂欲别求精义之功于洒扫应对以上。不止于实体上有析一为二之失。并用工处。将未免外事求理之病。下谕以二事为小大学习而察之之功。与夫洒扫精义一统处。实觉至当。不可移易。盖舍洒扫外。果别无讨个义处。自是一处做去。下面习得。上面察了。元无两段。然此义有更要子细在。所谓洒扫应对有所以然。精义入神有所以然者。恐是只就其然处。挈出所以然之理。似非以精义底不在洒扫之外。而便谓洒扫之所以然。乃精义之所以然也。何者。夫通天下是一贯底物事。不可分段。不可割裂。惟其事物之盈于天地者。不能无本末大小精粗浅深之别。是以。此理之寓
日间愦愦。无可振作。殊以为悯。世间事。又将如何了得。只有直截此心。趁此无事。拔出气力。窥见古人影象。循守古人涂辙。亦是所愿惟是。于实用工夫处。辄放下了。恐只是说耳。洒扫应对一段。反复下谕。参究论语本章近思录所论。行状尽性知命一条。才若有一个会通。庶可以不背。但犹有未尽释然者。谨略陈控。伏乞更有以开示焉。前者妄以事有本末。遂欲别求精义之功于洒扫应对以上。不止于实体上有析一为二之失。并用工处。将未免外事求理之病。下谕以二事为小大学习而察之之功。与夫洒扫精义一统处。实觉至当。不可移易。盖舍洒扫外。果别无讨个义处。自是一处做去。下面习得。上面察了。元无两段。然此义有更要子细在。所谓洒扫应对有所以然。精义入神有所以然者。恐是只就其然处。挈出所以然之理。似非以精义底不在洒扫之外。而便谓洒扫之所以然。乃精义之所以然也。何者。夫通天下是一贯底物事。不可分段。不可割裂。惟其事物之盈于天地者。不能无本末大小精粗浅深之别。是以。此理之寓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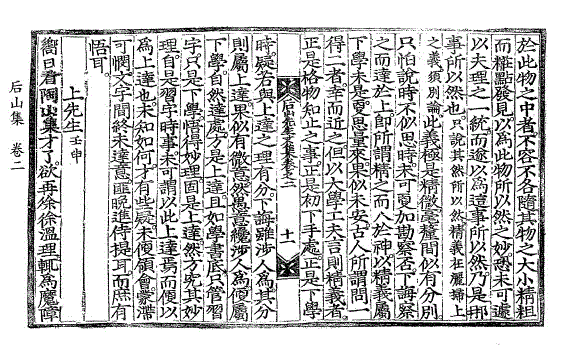 于此物之中者。不容不各随其物之大小精粗而妆点发见。以为此物所以然之妙。恐未可遽以夫理之一统。而遂以为这事所以然。乃是那事所以然也。(只说其然所以然。精义在洒扫上之义。须别论。)此义极是精微。毫釐间似有分别。只怕说时不似思时。未可更加勘察否。下诲察之而达于上。即所谓精之而入于神。以精义属下学未是。更思量来。果似未安。古人所谓问一得二者。幸而近之。但以大学工夫言则精义者。正是格物知止之事。正是初下手处。正是下学时。疑若与上达之理有分。下诲虽涉人为。其分则属上达。果似有微意。然愚意才涉人为。便属下学。自然达处。方是上达。且如学书底。只管习字。只是下学。悟得妙理。固是上达。然方究其妙理。自是习字时事。未可谓以此上达焉而便以为上达也。未知如何。才有些疑。未便领会。蒙滞可悯。文字间终未达意。匪晚进侍提耳。而庶有悟耳。
于此物之中者。不容不各随其物之大小精粗而妆点发见。以为此物所以然之妙。恐未可遽以夫理之一统。而遂以为这事所以然。乃是那事所以然也。(只说其然所以然。精义在洒扫上之义。须别论。)此义极是精微。毫釐间似有分别。只怕说时不似思时。未可更加勘察否。下诲察之而达于上。即所谓精之而入于神。以精义属下学未是。更思量来。果似未安。古人所谓问一得二者。幸而近之。但以大学工夫言则精义者。正是格物知止之事。正是初下手处。正是下学时。疑若与上达之理有分。下诲虽涉人为。其分则属上达。果似有微意。然愚意才涉人为。便属下学。自然达处。方是上达。且如学书底。只管习字。只是下学。悟得妙理。固是上达。然方究其妙理。自是习字时事。未可谓以此上达焉而便以为上达也。未知如何。才有些疑。未便领会。蒙滞可悯。文字间终未达意。匪晚进侍提耳。而庶有悟耳。上先生(壬申)
向日看陶山集才了。欲再徐徐温理。辄为魔障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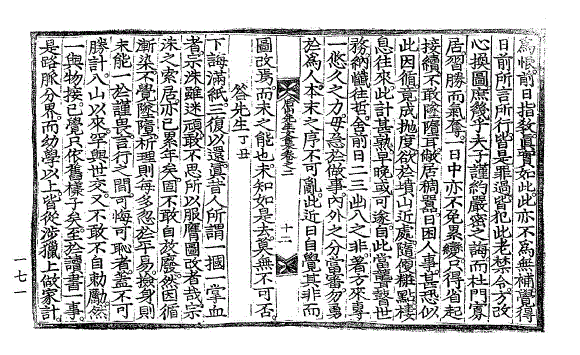 为恨。前日指教。真实如此。此亦不为无补。觉得日前所言所行。皆是罪过。皆犯此老禁令。方改心换图。庶几乎夫子谨约严密之诲。而杜门寡居。习胜而气夺。一日中亦不免累变。只得省起接续。不敢坠堕耳。敝居稠嚣。日困人事。甚恐似此因循。竟成抛度。欲于坟山近处。随便妆点。栖息往来。此计甚熟。早晚或可遂。自此当聋瞽世务。纳忏往哲。舍前日二三出入之非。著方来专一悠久之力。毋急于做事。内外之分当审。勿勇于为人。本末之序不可乱。此近日自觉其非而图改焉。而未之能也。未知如是去。莫无不可否。
为恨。前日指教。真实如此。此亦不为无补。觉得日前所言所行。皆是罪过。皆犯此老禁令。方改心换图。庶几乎夫子谨约严密之诲。而杜门寡居。习胜而气夺。一日中亦不免累变。只得省起接续。不敢坠堕耳。敝居稠嚣。日困人事。甚恐似此因循。竟成抛度。欲于坟山近处。随便妆点。栖息往来。此计甚熟。早晚或可遂。自此当聋瞽世务。纳忏往哲。舍前日二三出入之非。著方来专一悠久之力。毋急于做事。内外之分当审。勿勇于为人。本末之序不可乱。此近日自觉其非而图改焉。而未之能也。未知如是去。莫无不可否。答先生(丁丑)
下诲满纸。三复以还。真昔人所谓一掴一掌血者。宗洙虽迷顽。敢不思所以服膺图改者哉。宗洙之索居。亦已累年矣。固不敢自放废。然因循渐染。不觉坠堕。析理则每多忽于平易。捡身则未能一于谨畏。言行之间。可悔可耻者。盖不可胜计。入山以来。罕与世交。又不敢不自敕励。然一与物接。已觉只依旧样子矣。至于读书一事。是路脉分界。而幼学以上。皆从涉猎上做家计。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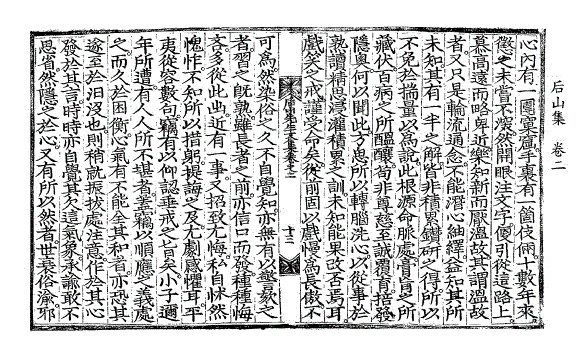 心内有一团窠窟。手里有一个伎俩。十数年来。惩之未尝不深。然开眼注文字。便引从这路上。慕高远而略卑近。乐知新而厌温故。其谓温故者。又只是轮流通念。不能潜心䌷绎。益知其所未知。其有一半之解。皆非积累钻研之得。所以不免于揣量以为说。此根源命脉处。膏肓之所藏伏。百病之所酝酿。苟非尊慈至诚覆育。掊发隐奥。何以闻此。方思所以转脑洗心。以从事于熟读精思浸灌积累之训。未知能果改否焉耳。戏笑之戒。谨受命矣。从前固以戏慢为长傲。不可为。然染俗之久不自觉知。亦无有以警欬之者。习之既熟。虽长者之前。亦信口而发。种种悔吝。多从此出。近有一事。又招致尤悔。私自怵然愧怍。不知所以措躬。提诲之及。尤剧感惧耳。平夷从容数句。窃有以仰认垂戒之旨矣。小子迩年所遭。有人人所不堪者。盖窃以顺应之义处之。而久于困衡。心气有不能全其和者。亦恐其遂至于汩没也。则稍就振拔处注意。作于其心发于其言。时时亦自觉其欠这气象。承谕敢不思省。然隐之于心。又有所以然者。世衰俗渝。邪
心内有一团窠窟。手里有一个伎俩。十数年来。惩之未尝不深。然开眼注文字。便引从这路上。慕高远而略卑近。乐知新而厌温故。其谓温故者。又只是轮流通念。不能潜心䌷绎。益知其所未知。其有一半之解。皆非积累钻研之得。所以不免于揣量以为说。此根源命脉处。膏肓之所藏伏。百病之所酝酿。苟非尊慈至诚覆育。掊发隐奥。何以闻此。方思所以转脑洗心。以从事于熟读精思浸灌积累之训。未知能果改否焉耳。戏笑之戒。谨受命矣。从前固以戏慢为长傲。不可为。然染俗之久不自觉知。亦无有以警欬之者。习之既熟。虽长者之前。亦信口而发。种种悔吝。多从此出。近有一事。又招致尤悔。私自怵然愧怍。不知所以措躬。提诲之及。尤剧感惧耳。平夷从容数句。窃有以仰认垂戒之旨矣。小子迩年所遭。有人人所不堪者。盖窃以顺应之义处之。而久于困衡。心气有不能全其和者。亦恐其遂至于汩没也。则稍就振拔处注意。作于其心发于其言。时时亦自觉其欠这气象。承谕敢不思省。然隐之于心。又有所以然者。世衰俗渝。邪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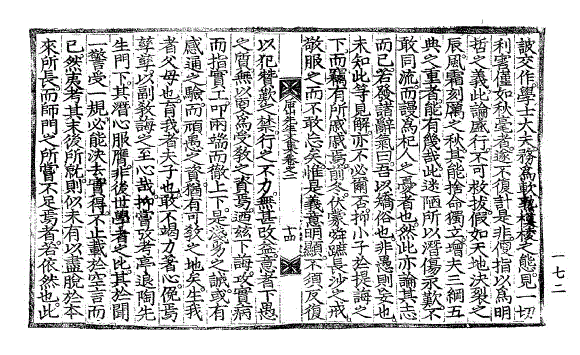 诐交作。学士大夫。务为软熟模棱之态。见一切利害仅如秋毫者。遂不复计是非。便指以为明哲之义。此论盛行。不可救拔。假如天地决裂之辰。风霜刻厉之秋。其能舍命独立。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者。能有几哉。此迷陋所以潜伤永叹。不敢同流。而谩为杞人之忧者也。然此亦论其志而已。若发诸辞气曰。吾以矫俗也。非愚则妄也。未知此等见解。亦不必尔否。抑小子于提诲之下。而窃有所戚戚焉。前冬。伏蒙舜蹠长沙之戒。敬服之而不敢忘矣。惟是义意明显。不须反复以犯赞叹之禁。行之不力。无甚改益。意者下愚之质。无以更为受教之资焉。乃玆下诲。攻实病而指实工。叩两端而彻上下。是浅劣之诚。或有感通之验。而顽愚之资。犹有可教之地矣。生我者父母也。育我者夫子也。敢不竭力著心。俛焉孳孳。以副教诲之至心哉。抑尝考考亭,退陶先生门下。其潜心服膺。非后世学者之比。其于闻一警受一规。必能决去实得。不止载于空言而已。然夷考其末后所就。则似未有以尽脱于本来所长。而师门之所尝不足焉者。若依然也。此
诐交作。学士大夫。务为软熟模棱之态。见一切利害仅如秋毫者。遂不复计是非。便指以为明哲之义。此论盛行。不可救拔。假如天地决裂之辰。风霜刻厉之秋。其能舍命独立。增夫三纲五典之重者。能有几哉。此迷陋所以潜伤永叹。不敢同流。而谩为杞人之忧者也。然此亦论其志而已。若发诸辞气曰。吾以矫俗也。非愚则妄也。未知此等见解。亦不必尔否。抑小子于提诲之下。而窃有所戚戚焉。前冬。伏蒙舜蹠长沙之戒。敬服之而不敢忘矣。惟是义意明显。不须反复以犯赞叹之禁。行之不力。无甚改益。意者下愚之质。无以更为受教之资焉。乃玆下诲。攻实病而指实工。叩两端而彻上下。是浅劣之诚。或有感通之验。而顽愚之资。犹有可教之地矣。生我者父母也。育我者夫子也。敢不竭力著心。俛焉孳孳。以副教诲之至心哉。抑尝考考亭,退陶先生门下。其潜心服膺。非后世学者之比。其于闻一警受一规。必能决去实得。不止载于空言而已。然夷考其末后所就。则似未有以尽脱于本来所长。而师门之所尝不足焉者。若依然也。此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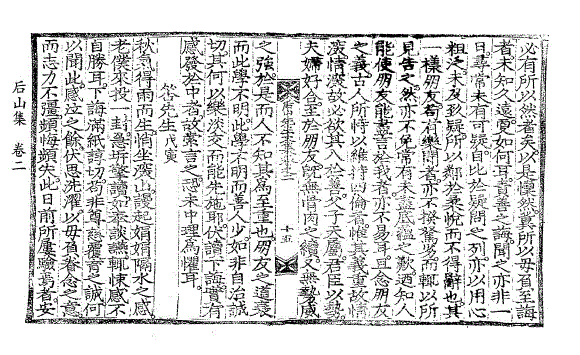 必有所以然者矣。以是懔然。冀所以毋负至诲者。未知久远。更如何耳。责善之诲。闻之亦非一日。寻常未有可疑。自比于疑问之列。亦以用心粗泛。未及致疑。所以邻于柔悦而不得辞也。其一样朋友。苟有乐闻者。亦不揆驽劣。而辄以所见告之。然亦不免常有未尽底蕴之叹。乃知人能使朋友能尽言于我者。亦不易耳。且念朋友之义。古人所恃以维持四伦者。惟其义重故情深。情深故必欲其入于善。父子天属。君臣以势。夫妇好合。至于朋友。既无骨肉之续。又无势威之强。于是而人不知其为至重也。朋友之道衰而此学不明。此学不明而善人少。如非自治诚切。其何以乐淡交而能先施耶。伏读下诲。实有感发于中者。故索言之。恐未中理为惧耳。
必有所以然者矣。以是懔然。冀所以毋负至诲者。未知久远。更如何耳。责善之诲。闻之亦非一日。寻常未有可疑。自比于疑问之列。亦以用心粗泛。未及致疑。所以邻于柔悦而不得辞也。其一样朋友。苟有乐闻者。亦不揆驽劣。而辄以所见告之。然亦不免常有未尽底蕴之叹。乃知人能使朋友能尽言于我者。亦不易耳。且念朋友之义。古人所恃以维持四伦者。惟其义重故情深。情深故必欲其入于善。父子天属。君臣以势。夫妇好合。至于朋友。既无骨肉之续。又无势威之强。于是而人不知其为至重也。朋友之道衰而此学不明。此学不明而善人少。如非自治诚切。其何以乐淡交而能先施耶。伏读下诲。实有感发于中者。故索言之。恐未中理为惧耳。答先生(戊寅)
秋气得雨而生。悄坐深山。谩起娟娟隔水之感。老仆来投一封。急坼擎读。如奉谈宴。辄悚感不自胜耳。下诲满纸谆切。苟非尊慈覆育之诚。何以闻此。感泣之馀。伏思洗濯。以毋负眷念之意。而志力不彊。频悔频失。此日前所屡验焉者。安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3L 页
 知异时之不如今日乎。青坪一款。盖不待事之既往。而已有不胜其悔者。一两月来。伏隩塞门。日省夕惕。庶几乎补复前非。而亦未有能也。致烦教诲。敢百拜而受之矣。且念先人平日处心行己。恬静守拙。视世之浮动喜事者。恶之若将浼焉。不肖不能谨守家训。未及三载。已犯其宿昔之所深恶。其为忝辱。孰大于是。思之汗怍。几无以自容耳。诱奖后进一段。是自家年来见。家内后生。一味忘学。无论向上。只此摘句工夫。亦无能如前辈之旧。居常悼叹。不免勉以其所明者。而不复以冷淡无味之说提耳而告之。以此之故。言论之间。未免有外内人己之分。不知后生益无复知有古人之教。则此言之罪也。儒者之道。一以贯之。心即是言。言即是事。由体而达用。成己以及物。岂可判内外作两端。分人己为二致。有如荆公高明中庸之论哉。此是索居钝滞。坠堕了处。蒙赐极本剖破。直发迷误。转移之机。匪由别人。洒脱之功。惟视方来耳。顾小子不自揣量。妄窃有意于学。亦已有年矣。伏蒙慈容曲赐提掖。所以感发兴起者。自谓千古以下无
知异时之不如今日乎。青坪一款。盖不待事之既往。而已有不胜其悔者。一两月来。伏隩塞门。日省夕惕。庶几乎补复前非。而亦未有能也。致烦教诲。敢百拜而受之矣。且念先人平日处心行己。恬静守拙。视世之浮动喜事者。恶之若将浼焉。不肖不能谨守家训。未及三载。已犯其宿昔之所深恶。其为忝辱。孰大于是。思之汗怍。几无以自容耳。诱奖后进一段。是自家年来见。家内后生。一味忘学。无论向上。只此摘句工夫。亦无能如前辈之旧。居常悼叹。不免勉以其所明者。而不复以冷淡无味之说提耳而告之。以此之故。言论之间。未免有外内人己之分。不知后生益无复知有古人之教。则此言之罪也。儒者之道。一以贯之。心即是言。言即是事。由体而达用。成己以及物。岂可判内外作两端。分人己为二致。有如荆公高明中庸之论哉。此是索居钝滞。坠堕了处。蒙赐极本剖破。直发迷误。转移之机。匪由别人。洒脱之功。惟视方来耳。顾小子不自揣量。妄窃有意于学。亦已有年矣。伏蒙慈容曲赐提掖。所以感发兴起者。自谓千古以下无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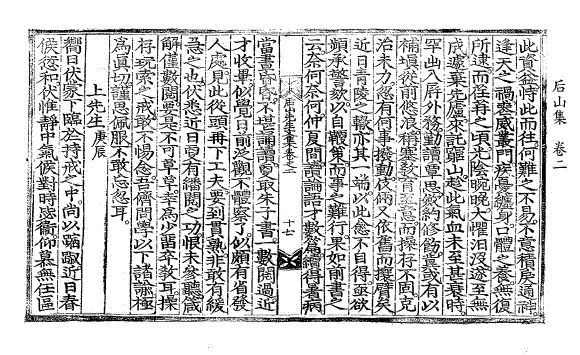 此资益。恃此而往。何难之不易。不意积戾通神。逢天之祸。丧威丛门。疾忧缠身。口体之养。无复所逮。而荏苒之顷。光阴晼晚。大惧汩没。遂至无成。遽弃先庐。来托穷山。趁此气血未至甚衰时。罕出入屏外务。勤读覃思。敛约修饬。冀或有以补填从前悠浪。称塞教育至意。而操存不固。克治未力。忽有何事拨动。伎俩又依旧而攘臂矣。近日青陵之辙。亦其一端。以此愈不自得。亟欲频承警欬。以自鞭策。而事之难行。果如前书之云。奈何奈何。仲夏间。读论语才数篇。续得暑病。当昼昏昏。不堪诵读。更取朱子书。一数阅过。近才收毕。似觉日前泛观不体察了。似颇有省发人处。见此从头再下工夫。要到贯熟。非敢有缓急之也。伏悉近日更有翻阅之功。恨未参听。箴解仅数阅。要是不可草草。幸为少留卒教耳。操存玩索之戒。敢不惕念。吾侪问学以下诸谕。极为真切。谨思佩服。不敢忘忽耳。
此资益。恃此而往。何难之不易。不意积戾通神。逢天之祸。丧威丛门。疾忧缠身。口体之养。无复所逮。而荏苒之顷。光阴晼晚。大惧汩没。遂至无成。遽弃先庐。来托穷山。趁此气血未至甚衰时。罕出入屏外务。勤读覃思。敛约修饬。冀或有以补填从前悠浪。称塞教育至意。而操存不固。克治未力。忽有何事拨动。伎俩又依旧而攘臂矣。近日青陵之辙。亦其一端。以此愈不自得。亟欲频承警欬。以自鞭策。而事之难行。果如前书之云。奈何奈何。仲夏间。读论语才数篇。续得暑病。当昼昏昏。不堪诵读。更取朱子书。一数阅过。近才收毕。似觉日前泛观不体察了。似颇有省发人处。见此从头再下工夫。要到贯熟。非敢有缓急之也。伏悉近日更有翻阅之功。恨未参听。箴解仅数阅。要是不可草草。幸为少留卒教耳。操存玩索之戒。敢不惕念。吾侪问学以下诸谕。极为真切。谨思佩服。不敢忘忽耳。上先生(庚辰)
向日伏蒙下临于持戒之中。尚以蹜踧。近日春候愆和。伏惟静中气候对时毖卫。仰慕无任区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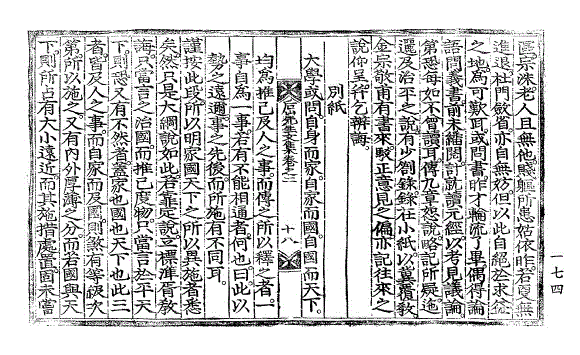 区。宗洙。老人且无他。贱躯所患姑依昨。若更无进退。杜门敛省。亦自无妨。但以此自绝于求益之地。为可叹耳。或问书。昨才轮流了毕。偶得论语问义书。前未翻阅。计就读元经。以考见议论。第恐每如不曾读耳。传九章恕说。略记所疑。迤逦及治平之说。有少劄录。录在小纸。以冀覆教。金宗敬甫有书来。驳正意见之偏。亦记往来之说仰呈。并乞辨诲。
区。宗洙。老人且无他。贱躯所患姑依昨。若更无进退。杜门敛省。亦自无妨。但以此自绝于求益之地。为可叹耳。或问书。昨才轮流了毕。偶得论语问义书。前未翻阅。计就读元经。以考见议论。第恐每如不曾读耳。传九章恕说。略记所疑。迤逦及治平之说。有少劄录。录在小纸。以冀覆教。金宗敬甫有书来。驳正意见之偏。亦记往来之说仰呈。并乞辨诲。别纸
大学或问。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均为推己及人之事。而传之所以释之者。一事自为一事。若有不能相通者。何也。曰。此以势之远迩。事之先后。而所施有不同耳。
谨按此段。所以明家国天下之所以异施者悉矣。然只是大纲说如此。若靠定说。立标准胥教诲。只当言之治国。而推己度物。只当言于平天下。则恐又有不然者。盖家也国也天下也此三者。皆及人之事。而自家而及国。则煞有等级次第。所以施之。又有内外厚薄之分。而若国与天下。则所占有大小远近。而其施措处置。固未尝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5H 页
 判然而为二也。且如治国之教成民法。固见其以推行为主。然必有以推己度物而后。使国内之人。得以遂其孝与弟之心矣。平天下之絜矩。是举此加彼之义。然依旧是因其兴仁兴让之化而裁之也。盖释者因经立传。故以末章别为一章。而其实言治国之道。而平天下之规模。寓于其中。不可以不察也。伏乞批诲。
判然而为二也。且如治国之教成民法。固见其以推行为主。然必有以推己度物而后。使国内之人。得以遂其孝与弟之心矣。平天下之絜矩。是举此加彼之义。然依旧是因其兴仁兴让之化而裁之也。盖释者因经立传。故以末章别为一章。而其实言治国之道。而平天下之规模。寓于其中。不可以不察也。伏乞批诲。答。所论甚善。当如此看。盖家国天下。虽有远近先后之分。而初无二道云云。今以国与天下为无二致。而以家国为有别则亦恐有未尽也。盖家是小底国。国是大底家。随其大小之势。而所施有厚薄。国与天下。亦以远近之异。而有详略广狭之分。今谓因经立传(止)寓于其中则是此一章。为无用之赘言。而有亦可无亦可耳。乌乎可哉。大抵家国天下。其分虽殊而理则一。又不可以理之一而遂废其分之殊。须是两下看破。方是绝渗漏。无病败耳。
权炳甫有书云论语为仁之本章。程子说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曷尝有孝弟来。此固然矣。然若说有时。万理俱有。若说无时。性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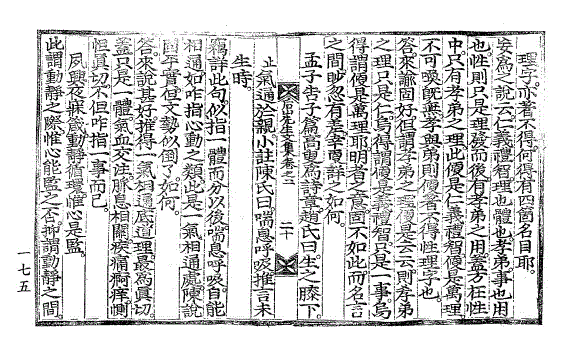 理字。亦著不得。何得有四个名目耶。
理字。亦著不得。何得有四个名目耶。妄为之说云。仁义礼智。理也体也。孝弟。事也用也。性则只是理发而后。有孝弟之用。盖方在性中。只有孝弟之理。此便是仁义礼智。便是万理。不可唤既无。孝与弟则便著不得性理字也。
答。来谕固好。但谓孝弟之理便是云云。则孝弟之理只是仁。乌得谓便是义礼智。只是一事。乌得谓便是万理耶。明者之意。固不如此。而名言之间。眇忽有差。幸更详之如何。
孟子告子篇高叟为诗章。赵氏曰。生之膝下。(止)气通于亲。小注陈氏曰。喘息呼吸。推言未生时。
窃详此句。似指一体而分以后。喘息呼吸。自能相通。如咋指心动之类。此是一气相通处。陈说固平实。但文势似倒了。如何。
答。来说甚好。推得一气相通底道理。最为真切。盖只是一体。气血交注。脉息相关。疾痛痾痒。恻怛真切。不但咋指一事而已。
夙兴夜寐箴。动静循环。惟心是监。
此谓动静之际。惟心能监之否。抑谓动静之间。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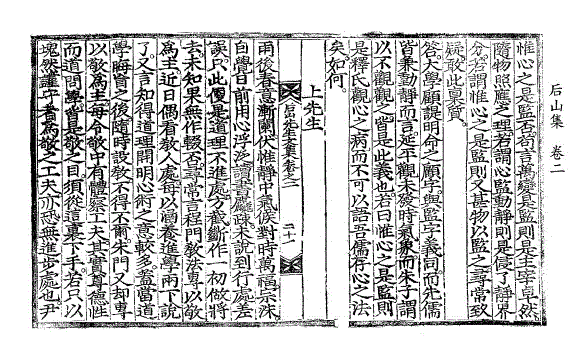 惟心之是监否。苟言万变是监则是主宰卓然。随物照应之理。若谓心监动静则是侵了静界分。若谓惟心之是监则又甚物以监之。寻常致疑。敢此禀质。
惟心之是监否。苟言万变是监则是主宰卓然。随物照应之理。若谓心监动静则是侵了静界分。若谓惟心之是监则又甚物以监之。寻常致疑。敢此禀质。答。大学顾諟明命之顾字。与监字义同。而先儒皆兼动静而言。延平观未发时气象。而朱子谓以不观观之。皆是此义也。若曰惟心之是监。则是释氏观心之病。而不可以语吾儒存心之法矣。如何。
上先生
雨后春意渐阑。伏惟静中气候对时万福。宗洙。自觉日前用心浮泛。读书粗疏。未说到行处差误。只此便是道理不进处。方截断作一初做将去。未知果无作辍否。寻常言程门教法专以敬为主。近日偶看教人处。每以涵养进学两下说了。又言知得道理开明心术之意较多。盖当道学晦盲之后。随时设教。不得不尔。朱门又却专以敬为主。每令敬中有体察工夫。其实尊德性而道问学。皆是敬之目。须从这里下手。若只以块然谨守者为敬之工夫。亦恐无进步处也。尹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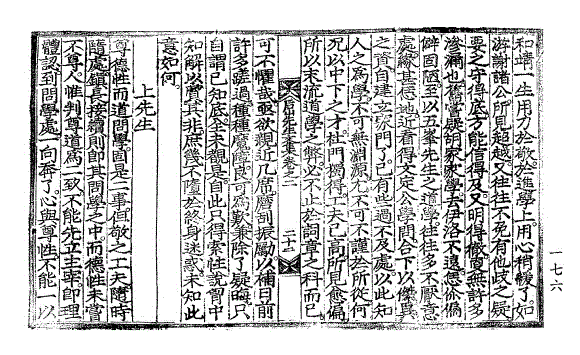 和靖一生用力于敬。于进学上。用心稍缓了。如游谢诸公。所见超越。又往往不免有他歧之疑。要之守得底。方能信得及。又明得彻。更无许多渗漏也。旧尝疑胡家家学。去伊洛不远。恁你偏僻固陋。至以五峰先生之道学。往往多不厌意处。缘甚恁地。近看得文定公学问。合下以杰异之资。自建立家门了。已有些过不及处。以此知人之为学。不可无渊源。尤不可不谨于所从。何况以中下之才。杜门独得。工夫已高。所见愈偏。所以末流道学之弊。必不止于词章之科而已。可不惧哉。亟欲亲近几席。磨刮振励。以补日前许多蹉过。种种魔障。良可为叹。兼除了疑晦。只自谓已知底。全未睹是。自此只得索性说胸中知解以质其非。庶几不堕于终身迷惑。未知此意如何。
和靖一生用力于敬。于进学上。用心稍缓了。如游谢诸公。所见超越。又往往不免有他歧之疑。要之守得底。方能信得及。又明得彻。更无许多渗漏也。旧尝疑胡家家学。去伊洛不远。恁你偏僻固陋。至以五峰先生之道学。往往多不厌意处。缘甚恁地。近看得文定公学问。合下以杰异之资。自建立家门了。已有些过不及处。以此知人之为学。不可无渊源。尤不可不谨于所从。何况以中下之才。杜门独得。工夫已高。所见愈偏。所以末流道学之弊。必不止于词章之科而已。可不惧哉。亟欲亲近几席。磨刮振励。以补日前许多蹉过。种种魔障。良可为叹。兼除了疑晦。只自谓已知底。全未睹是。自此只得索性说胸中知解以质其非。庶几不堕于终身迷惑。未知此意如何。上先生
尊德性而道问学。固是二事。但敬之工夫。随时随处。镇长接续则即其问学之中。而德性未尝不尊。人惟判尊道为二致。不能先立主宰。即理体认。到问学处。一向奔了。心与尊性。不能一以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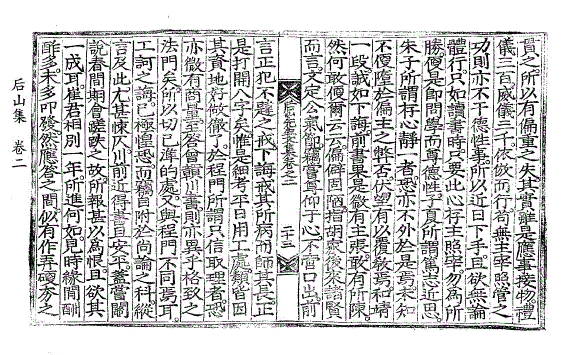 贯之。所以有偏重之失。其实虽是应事接物。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依仿而行。苟无主宰照管之功则亦不干德性事。所以近日下手。且欲无论体行。只如读书时。只要此心存主照宰。勿为所胜。便是即问学而尊德性。子夏所谓笃志近思。朱子所谓存心静一者。恐亦不外于是焉。未知不便堕于偏主之弊否。伏望有以覆教焉。和靖一段。诚如下诲。前书果是微有主张。敢有所陈。然何敢便尔云云。偏僻固陋。指胡家后来诸贤而言。文定公气节。窃尝尊仰于心。不啻口出。前言正犯不韪之戒。下诲戒其所病而师其长。正是打开八字矣。惟是细考平日用工处。类皆因其资地好做彻了。于程门所谓只信取理者。恐亦微有商量。至答曾赣川书。则亦异乎格致之法门矣。所以切己准的处。又与程门不同焉耳。工诃之诲。已极惶恐。而窃自附于尚论之科。纵言及此。尤甚悚仄。川前近得书且安平。盖尝关说春间期会蹉跌之故。所报甚以为恨。且欲其一成耳。崔君相别一年。所进何如。见时缘閒酬酢多。未多叩发。然应答之间。似有作弄硬夯之
贯之。所以有偏重之失。其实虽是应事接物。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依仿而行。苟无主宰照管之功则亦不干德性事。所以近日下手。且欲无论体行。只如读书时。只要此心存主照宰。勿为所胜。便是即问学而尊德性。子夏所谓笃志近思。朱子所谓存心静一者。恐亦不外于是焉。未知不便堕于偏主之弊否。伏望有以覆教焉。和靖一段。诚如下诲。前书果是微有主张。敢有所陈。然何敢便尔云云。偏僻固陋。指胡家后来诸贤而言。文定公气节。窃尝尊仰于心。不啻口出。前言正犯不韪之戒。下诲戒其所病而师其长。正是打开八字矣。惟是细考平日用工处。类皆因其资地好做彻了。于程门所谓只信取理者。恐亦微有商量。至答曾赣川书。则亦异乎格致之法门矣。所以切己准的处。又与程门不同焉耳。工诃之诲。已极惶恐。而窃自附于尚论之科。纵言及此。尤甚悚仄。川前近得书且安平。盖尝关说春间期会蹉跌之故。所报甚以为恨。且欲其一成耳。崔君相别一年。所进何如。见时缘閒酬酢多。未多叩发。然应答之间。似有作弄硬夯之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7L 页
 意。亦是一病。亦不免微致其意。未知能领察否。大抵彼中朋友立作处为可服耳。金溪权戚煞有用心。所见多精到。甚为不易。但养得来偏了。求理亦多就尖斜苦涩处去。不是细病。已向渠苦口。第觉用力稍深。家计渐成。翻转得须不易。又初学时用心极苦。耗了心力。似欠了点开二子底意思。此尤非一枝一叶之病耳。俟病稣进谒。
意。亦是一病。亦不免微致其意。未知能领察否。大抵彼中朋友立作处为可服耳。金溪权戚煞有用心。所见多精到。甚为不易。但养得来偏了。求理亦多就尖斜苦涩处去。不是细病。已向渠苦口。第觉用力稍深。家计渐成。翻转得须不易。又初学时用心极苦。耗了心力。似欠了点开二子底意思。此尤非一枝一叶之病耳。俟病稣进谒。别纸
前说。论及子贡终身之恕。未蒙剖破是自治是及人底。等是爱人之事。亦当以及人底看去否。盖子贡当初非是问崇德修慝之事。只问可以行于外者。所以把推己及人处。说与爱人之道。未知是否。
答。子贡终身之恕。前蒙谕及。以非本意所关。不及奉浼。致烦再叩。大抵既曰终身而行。则有多少事在。治人爱人。皆兼包在里。岂可说是治人是爱人耶。崇德修慝。方是做忠底事。未可唤做恕也。
家国天下此段。亦闻命矣。但国与天下。虽有远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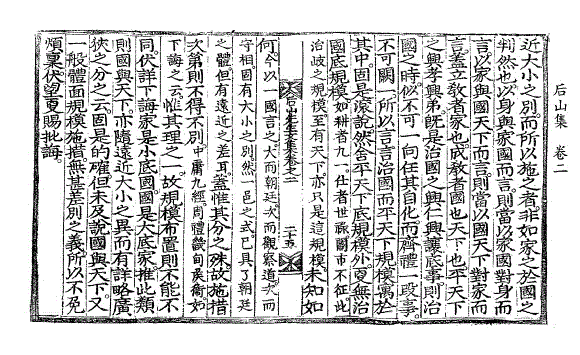 近大小之别。而所以施之者。非如家之于国之判然也。以身与家国而言。则当以家国对身而言。以家与国天下而言。则当以国天下对家而言。盖立教者家也。成教者国也天下也。平天下之兴孝兴弟。既是治国之兴仁兴让底事。则治国之时。似不可一向任其自化。而齐礼一段事。不可阙一。所以言言治国而平天下规模寓于其中。固是滚说。然舍平天下底规模外。更无治国底规模。(如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不征。此治岐之规模。至有天下。亦只是这规模。)未知如何。(今以一国言之。大而朝廷。次而观察道。次而守相。固有大小之别。然一邑之式。已具了朝廷之体。但有远近之差耳。)盖惟其分之殊。故施措次第则不得不别。(中庸九经。周礼畿甸侯卫。如下诲之云。)惟其理之一。故规模布置则不能不同。伏详下诲家是小底国。国是大底家。推此类则国与天下。亦随远近大小之异而有详略广狭之分之云。固是的确。但未及说国与天下。又一般体面规模施措。无甚差别之义。所以不免烦禀。伏望更赐批诲。
近大小之别。而所以施之者。非如家之于国之判然也。以身与家国而言。则当以家国对身而言。以家与国天下而言。则当以国天下对家而言。盖立教者家也。成教者国也天下也。平天下之兴孝兴弟。既是治国之兴仁兴让底事。则治国之时。似不可一向任其自化。而齐礼一段事。不可阙一。所以言言治国而平天下规模寓于其中。固是滚说。然舍平天下底规模外。更无治国底规模。(如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不征。此治岐之规模。至有天下。亦只是这规模。)未知如何。(今以一国言之。大而朝廷。次而观察道。次而守相。固有大小之别。然一邑之式。已具了朝廷之体。但有远近之差耳。)盖惟其分之殊。故施措次第则不得不别。(中庸九经。周礼畿甸侯卫。如下诲之云。)惟其理之一。故规模布置则不能不同。伏详下诲家是小底国。国是大底家。推此类则国与天下。亦随远近大小之异而有详略广狭之分之云。固是的确。但未及说国与天下。又一般体面规模施措。无甚差别之义。所以不免烦禀。伏望更赐批诲。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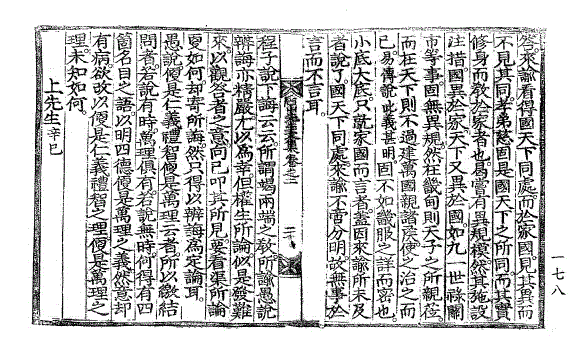 答。来谕看得国天下同处。而于家国。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孝弟慈固是国天下之所同。而其实修身而教于家者也。曷尝有异规模。然其施设注措。国异于家。天下又异于国。如九一世禄关市等事。固无异规。然在畿甸则天子之所亲莅。而在天下则不过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治之而已。(易传说此义甚明。)固不如畿服之详而密也。小底大底。只就家国而言者。盖因来谕所未及者说了。国天下同处。来谕不啻分明。故无事于言而不言耳。
答。来谕看得国天下同处。而于家国。见其异而不见其同。孝弟慈固是国天下之所同。而其实修身而教于家者也。曷尝有异规模。然其施设注措。国异于家。天下又异于国。如九一世禄关市等事。固无异规。然在畿甸则天子之所亲莅。而在天下则不过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治之而已。(易传说此义甚明。)固不如畿服之详而密也。小底大底。只就家国而言者。盖因来谕所未及者说了。国天下同处。来谕不啻分明。故无事于言而不言耳。程子说下诲云云。所谓竭两端之教。所谕愚说辨诲亦精严。尤以为幸。但权生所论。似是发难来。以观答者之意。向已叩其所见。要看渠所论更如何。却寄所诲。然只得以辨诲为定论耳。
愚说。便是仁义礼智便是万理云者。所以缴结问者。若说有时。万理俱有。若说无时。何得有四个名目之语。以明四德便是万理之义。然意却有病。欲改以便是仁义礼智之理。便是万理之理。未知如何。
上先生(辛巳)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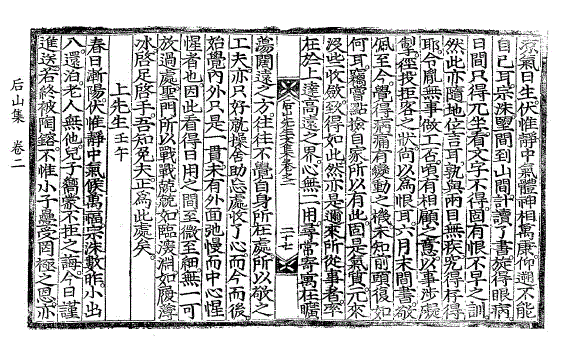 凉气日生。伏惟静中气体神相万康。仰溯不能自已耳。宗洙。望间到山间。计读了书。旋得眼病。日间只得兀坐。看文字不得。固有恨不早之训。然此亦随地位言耳。孰与两目无疾。究得存得耶。令胤无事做工否。顷有相顾之意。以事涉碍掣。径投拒客之状。尚以为恨耳。六月末间书。敬佩至今。觉得病痛有变动之机。未知前头复如何耳。窃尝点捡自家所以有此。固是气质。元来没些收敛。致得如此。然亦是迩来所从事者。率在于上达高远之界。心无二用。寻常寄寓在旷荡阔远之方。往往不觉自身所在处。所以敬之工夫。亦只好就操舍助忘处收了心。而今而后。始觉内外只是一贯。未有外面弛慢而中心惺惺者也。因此看得日用之间至微至细。无一可放过处。圣门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启足启手。吾知免夫。正为此处矣。
凉气日生。伏惟静中气体神相万康。仰溯不能自已耳。宗洙。望间到山间。计读了书。旋得眼病。日间只得兀坐。看文字不得。固有恨不早之训。然此亦随地位言耳。孰与两目无疾。究得存得耶。令胤无事做工否。顷有相顾之意。以事涉碍掣。径投拒客之状。尚以为恨耳。六月末间书。敬佩至今。觉得病痛有变动之机。未知前头复如何耳。窃尝点捡自家所以有此。固是气质。元来没些收敛。致得如此。然亦是迩来所从事者。率在于上达高远之界。心无二用。寻常寄寓在旷荡阔远之方。往往不觉自身所在处。所以敬之工夫。亦只好就操舍助忘处收了心。而今而后。始觉内外只是一贯。未有外面弛慢而中心惺惺者也。因此看得日用之间至微至细。无一可放过处。圣门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启足启手。吾知免夫。正为此处矣。上先生(壬午)
春日渐阳。伏惟静中气候万福。宗洙数昨。小出入。还泊。老人无他。儿子向蒙不拒之诲。今日谨进送。若终被陶镕。不惟小子叠受罔极之恩。亦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79L 页
 门户永获无穷之赐矣。
门户永获无穷之赐矣。答先生(甲申)
春寒。静里气候对时万安。玩心神明。日有新益。此后生之所仰叹而俛学焉者也。宗洙。馈奠之馀。非无暇隙。而专阙见成功夫。日间或料理论语。而且以旧时读得。每于下一半草率。今且截从后面生硬处试手。以约课多遍为法。始觉从前用志浮泛。不能刻意用工。所以因循差池。不知年岁之往。日夕凛然。盖未知所以措其躬耳。观礼之戒。敢不铭服。当初只要收了前人未了底头绪。枉费日月。见今略成头尾。至于刊节之事。容俟具眼。亦罢休已累月矣。
别纸
论语。子贡问管仲不能死章程子说。 语类。问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说。朱子曰。前说亦是可。但自免以图后功则可之大者。又问孟子可以死可以无死。始见其可以死。后细思之。又见其可以无死。则前之可者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
窃谓程子两可也。正谓死与图功为两可耳。非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0H 页
 谓与之同死似可。而自免图功为真可也。子贡以相桓图功为未仁。故夫子以徒死为匹夫之谅。而明其图功之未为不仁。盖管仲辅之争。已害于义。若悔其失而图后功。则其不死也非爱死也。而其图功足以补其辅之争之失也。若自度其才不足以图后功。则亦有死而已。岂可以始焉辅之非义。而见其死而背之。正所以启万世忘君苟生之弊也。观程朱议论。见于本章小注中。(注中一条。是或问说。)未尝以召忽之死为不得其死。则仲之与同死。岂不可哉。或者以夫子自经沟渎之训。至比召忽之死于匹夫之谅。似失圣人抑扬之意矣。孟子所谓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乃谓初若可死而再思之。真不可死者也。其义与此似别。末段问答。恐当更商。未知如何。
谓与之同死似可。而自免图功为真可也。子贡以相桓图功为未仁。故夫子以徒死为匹夫之谅。而明其图功之未为不仁。盖管仲辅之争。已害于义。若悔其失而图后功。则其不死也非爱死也。而其图功足以补其辅之争之失也。若自度其才不足以图后功。则亦有死而已。岂可以始焉辅之非义。而见其死而背之。正所以启万世忘君苟生之弊也。观程朱议论。见于本章小注中。(注中一条。是或问说。)未尝以召忽之死为不得其死。则仲之与同死。岂不可哉。或者以夫子自经沟渎之训。至比召忽之死于匹夫之谅。似失圣人抑扬之意矣。孟子所谓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乃谓初若可死而再思之。真不可死者也。其义与此似别。末段问答。恐当更商。未知如何。无可无不可集注。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云云。
窃尝见小注。皆以无字作心上说。如曰方其事未定时。此心无可无不可。及其事已断后。有可有不可云云。谓夫子则异于是。心未尝先有可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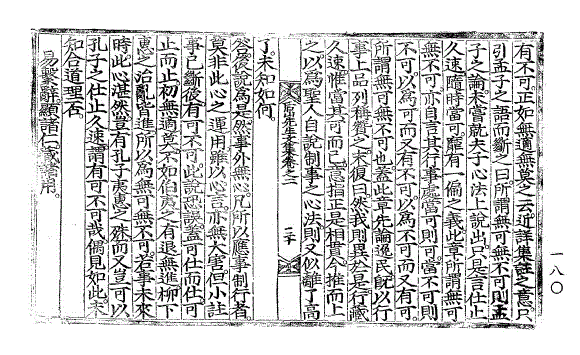 有不可。正如无适无莫之云。近详集注之意。只引孟子之语而断之曰。所谓无可无不可则孟子之论。未尝就夫子心法上说出。只是言仕止久速。随时当可。靡有一偏之义。此章所谓无可无不可。亦自言其行事处当可则可。当不可则不可。以为可而又有不可。以为不可而又有可。所谓无可无不可也。盖此章先论逸民。既以行事上品列称赞之。末复曰。然我则异于是。行藏久速。惟当其可而已。意指正是相贯。今推而上之。以为圣人自说制事之心法。则又似离了高了。未知如何。
有不可。正如无适无莫之云。近详集注之意。只引孟子之语而断之曰。所谓无可无不可则孟子之论。未尝就夫子心法上说出。只是言仕止久速。随时当可。靡有一偏之义。此章所谓无可无不可。亦自言其行事处当可则可。当不可则不可。以为可而又有不可。以为不可而又有可。所谓无可无不可也。盖此章先论逸民。既以行事上品列称赞之。末复曰。然我则异于是。行藏久速。惟当其可而已。意指正是相贯。今推而上之。以为圣人自说制事之心法。则又似离了高了。未知如何。答。后说为是。然事外无心。凡所以应事制行者。莫非此心之运用。虽以心言。亦无大害。但小注事已断后。有可不可。此说恐误。盖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初无适莫。不如伯夷之有退无进。柳下惠之治乱皆进。所以为无可无不可。若事未来时。此心湛然。岂有孔子夷惠之殊。而又岂可以孔子之仕止久速。谓有可不可哉。偶见如此。未知合道理否。
易系辞。显诸仁。藏诸用。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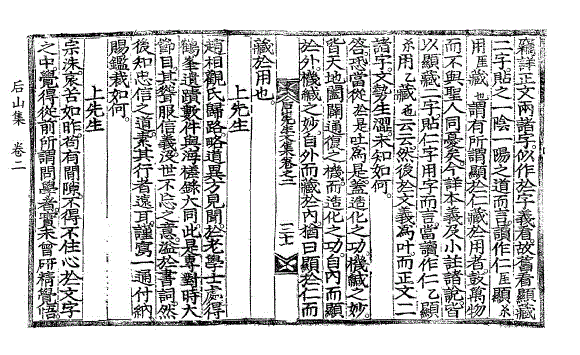 窃详正文两诸字。似作于字义看。故旧看显藏二字。贴之一阴一阳之道而言。读作仁()显()用()藏()谓有所谓显于仁藏于用者。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矣。今详本义及小注诸说。皆以显藏二字。贴仁字用字而言。当读作仁()显()用()藏()云云。然后于文义为叶。而正文二诸字。文势生涩。未知如何。
窃详正文两诸字。似作于字义看。故旧看显藏二字。贴之一阴一阳之道而言。读作仁()显()用()藏()谓有所谓显于仁藏于用者。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矣。今详本义及小注诸说。皆以显藏二字。贴仁字用字而言。当读作仁()显()用()藏()云云。然后于文义为叶。而正文二诸字。文势生涩。未知如何。答。恐当从于是吐为是。盖造化之功。机缄之妙。皆天地阖辟通复之机。而造化之功。自内而显于外。机缄之妙。自外而藏于内。犹曰显于仁而藏于用也。
上先生
赵相观氏归路。略道异方见闻。于老学士处得鹤峰遗迹数件与海槎录大同。此是专对时大节目。其耸服信义。没世不忘之意。溢于书词。然后知忠信之道。素其行者远耳。谨写一通付纳。赐鉴裁如何。
上先生
宗洙。哀苦如昨。苟有閒隙。不得不住心于文字之中。觉得从前所谓问学者。实未曾研精觉悟。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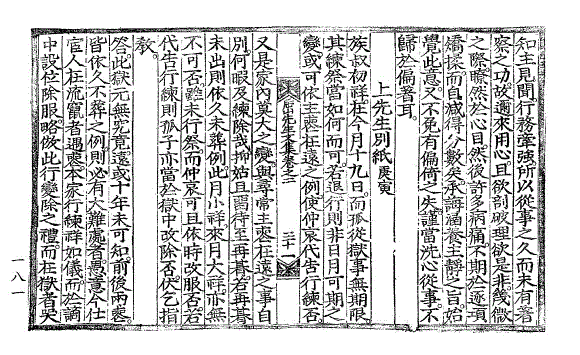 知主见闻。行务牵强。所以从事之久而未有著察之功。故迩来用心。且欲剖破理欲是非。几微之际。瞭然于心目。然后许多病痛。不期于逐项矫揉。而自减得分数矣。承诲涵养主静之旨。始觉此意。又不免有偏倚之失。谨当洗心从事。不归于偏著耳。
知主见闻。行务牵强。所以从事之久而未有著察之功。故迩来用心。且欲剖破理欲是非。几微之际。瞭然于心目。然后许多病痛。不期于逐项矫揉。而自减得分数矣。承诲涵养主静之旨。始觉此意。又不免有偏倚之失。谨当洗心从事。不归于偏著耳。上先生别纸(庚寅)
族叔初祥。在今月十九日。而孤从狱事无期限。其练祭当如何而可。若退行则非日月可期之变。或可依主丧在远之例。使仲哀代告行练否。又是家内莫大之变。与寻常主丧在远之事自别。何暇及练除哉。抑姑且留待至再期。若再期未出则依久未葬例。此月小祥。来月大祥。亦无不可否。虽未行祭。而仲哀可且依时改服否。若代告行练则孤子亦当于狱中改除否。伏乞指教。
答。此狱元无究竟。远或十年未可知。前后两丧。皆依久不葬之例。则必有大难处者。愚意今仕宦人在流窜者遇丧。本家行练祥如仪。而于谪中设位除服。略仿此行变除之礼。而在狱者哭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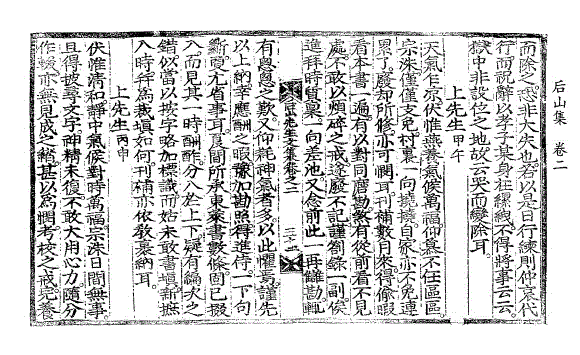 而除之。恐非大失也。若以是日行练则仲哀代行。而祝辞以孝子某身在缧绁。不得将事云云。狱中非设位之地。故云哭而变除耳。
而除之。恐非大失也。若以是日行练则仲哀代行。而祝辞以孝子某身在缧绁。不得将事云云。狱中非设位之地。故云哭而变除耳。上先生(甲午)
天气乍凉。伏惟燕养气候万福。仰慕不任区区。宗洙。仅仅支免。村里一向挠挠。自家亦不免连累了。废却所修。亦可悯耳。刊补数月来。得偷暇看本书一遍。有以对同磨勘。煞有从前看不见处。不敢以烦碎之戒。遂废不记。谨劄录一副。俟进拜时质禀。一向差池。又念前此一再雠勘。辄有悤悤之叹。又仰耗神气者多。以此惧焉。谨先以上纳。幸应酬之暇。豫加勘照。得进侍。一下句断。更尤省事耳。夏间所承东莱书数条。固已掇入。而见其一时酬酢。分入于上下。疑有编次之错。似当以按字略加标识。而姑未敢书填。新摭入时。并为裁填如何。刊补亦依教裹纳耳。
上先生(丙申)
伏惟清和。静中气候对时万福。宗洙日间无事。且得披寻文字。神精未复。不敢大用心力。随分作辍。亦无见成之绪。甚以为悯。考校之戒。完养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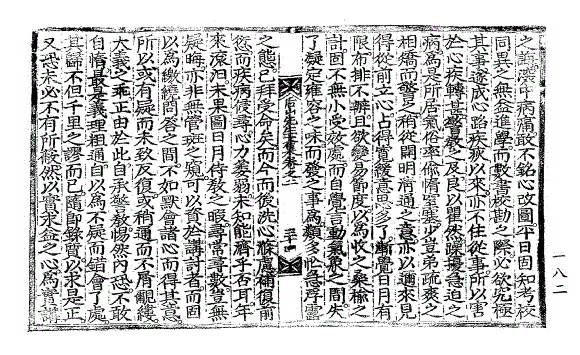 之诲。深中病痛。敢不铭心改图。平日固知考校同异之无益进学。而数书校勘之际。必欲究极其事。遂成心路疾疢以来。亦不住从事。所以害于心疾转甚。警教之及。良以瞿然。躁扰急迫之病。为是所居气俗率偷惰窒塞。少岂弟疏爽之相矫而警之。稍从开明清通之意。亦以迩来见得从前立心。占得宽缓意思多了。渐觉日月有限。布排不办。且欲变易节度。以为收之桑榆之计。固不无小受效处。而自觉言动气象之间。失了凝定雍容之味。而发之事为。类多忙急浮露之态。已拜受命矣。而今而后洗心涤虑。补复前愆。而疾病侵寻。心力萎弱。未知能济乎否耳。年来滚汩。未果图日月侍教之暇。寻常寻数。岂无疑晦。亦非无管斑之窥。可以资于讲讨者。而固以为缴绕问答之间。不如默会诸心而得其意。所以或有疑而未致反复。或稍通而不屑覼缕。大义之乖。正由于此。自承警教。惕然内恐。不敢自惰。最是义理粗通。自以为不疑而错会了处。其归不但千里之谬而已。随即录质。以求是正。又恐未必不有所蔽。然以实求益之心。为实讲
之诲。深中病痛。敢不铭心改图。平日固知考校同异之无益进学。而数书校勘之际。必欲究极其事。遂成心路疾疢以来。亦不住从事。所以害于心疾转甚。警教之及。良以瞿然。躁扰急迫之病。为是所居气俗率偷惰窒塞。少岂弟疏爽之相矫而警之。稍从开明清通之意。亦以迩来见得从前立心。占得宽缓意思多了。渐觉日月有限。布排不办。且欲变易节度。以为收之桑榆之计。固不无小受效处。而自觉言动气象之间。失了凝定雍容之味。而发之事为。类多忙急浮露之态。已拜受命矣。而今而后洗心涤虑。补复前愆。而疾病侵寻。心力萎弱。未知能济乎否耳。年来滚汩。未果图日月侍教之暇。寻常寻数。岂无疑晦。亦非无管斑之窥。可以资于讲讨者。而固以为缴绕问答之间。不如默会诸心而得其意。所以或有疑而未致反复。或稍通而不屑覼缕。大义之乖。正由于此。自承警教。惕然内恐。不敢自惰。最是义理粗通。自以为不疑而错会了处。其归不但千里之谬而已。随即录质。以求是正。又恐未必不有所蔽。然以实求益之心。为实讲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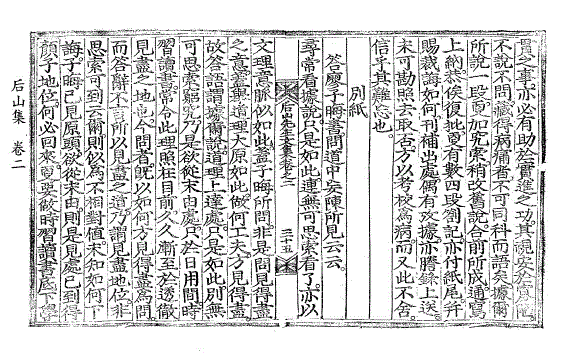 贯之事。亦必有助于实进之功。其视安于寡陋。不说不问。藏得病痛者。不可同科而语矣。据尔所说一段。更加究索。稍改旧说。合前所成。通写上纳。恭俟复批。更有数四段劄记。亦付纸尾。并赐裁诲如何。刊补出处。偶有考据。亦誊录上送。未可勘照去取否。方以考校为病。而又此不舍。信乎其难忘也。
贯之事。亦必有助于实进之功。其视安于寡陋。不说不问。藏得病痛者。不可同科而语矣。据尔所说一段。更加究索。稍改旧说。合前所成。通写上纳。恭俟复批。更有数四段劄记。亦付纸尾。并赐裁诲如何。刊补出处。偶有考据。亦誊录上送。未可勘照去取否。方以考校为病。而又此不舍。信乎其难忘也。别纸
答廖子晦书。问道中妄陈所见云云。
寻常看据说。只是如此。连无可思索看了。亦以文理意脉似如此。盖子晦所问。非是问见得尽之意。盖举道理大原如此。做何工夫。方见得尽。故答语谓据尔说。道理上达处。只是如此。别无可思索穷究。乃是欲从末由处。只于日用间。时习读书。常令此理照在目前。久久渐至于透彻见尽之地也。今问者。既以如何方见得尽为问。而答辞不言所以见尽之道。乃谓见尽地位。非思索可到云尔。则似为不相对值。未知如何下诲。子晦已见原头。欲从末由。则是见处已到得颜子地位。何必回来。更要做时习读书底下学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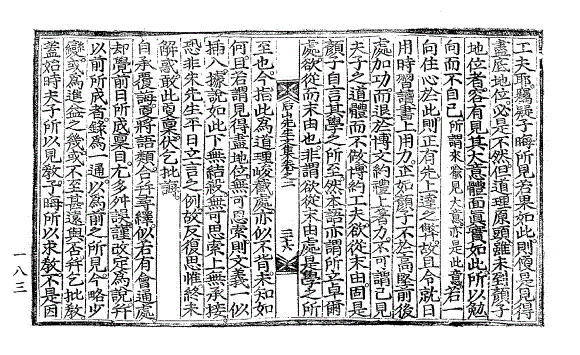 工夫耶。窃疑子晦所见若果如此。则便是见得尽底地位。必是不然。但道理原头。虽未到颜子地位者。容有见其大意体面真实如此。所以勉向而不自已。(所谓来喻见大意。亦是此意。)若一向住心于此。则正有先上达之弊。故且令就日用时习读书上用力。正如颜子不于高坚前后处加功。而退于博文约礼上著力。不可谓已见夫子之道体而不做博约工夫。欲从末由。固是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然本语亦谓所立卓尔处。欲从而末由也。非谓欲从末由处是学之所至也。今指此为道理峻截处。亦似不背。未知如何。且若谓见得尽地位。无可思索。则文义一似插入。据说如此下无结杀。无可思索上无承接。恐非朱先生平日立言之例。故反复思惟。终未解惑。敢此更禀。伏乞批诲。
工夫耶。窃疑子晦所见若果如此。则便是见得尽底地位。必是不然。但道理原头。虽未到颜子地位者。容有见其大意体面真实如此。所以勉向而不自已。(所谓来喻见大意。亦是此意。)若一向住心于此。则正有先上达之弊。故且令就日用时习读书上用力。正如颜子不于高坚前后处加功。而退于博文约礼上著力。不可谓已见夫子之道体而不做博约工夫。欲从末由。固是颜子自言其学之所至。然本语亦谓所立卓尔处。欲从而末由也。非谓欲从末由处是学之所至也。今指此为道理峻截处。亦似不背。未知如何。且若谓见得尽地位。无可思索。则文义一似插入。据说如此下无结杀。无可思索上无承接。恐非朱先生平日立言之例。故反复思惟。终未解惑。敢此更禀。伏乞批诲。自承覆诲。更将语类。合并寻绎。似若有会通处。却觉前日所成禀目。尤多舛误。谨改定为说。并以前所成者。录为一通。以为前之所见。今略少变。或为进益之几。或不至甚远与否。并乞批教。盖始时夫子所以见教。子晦所以求教。不是因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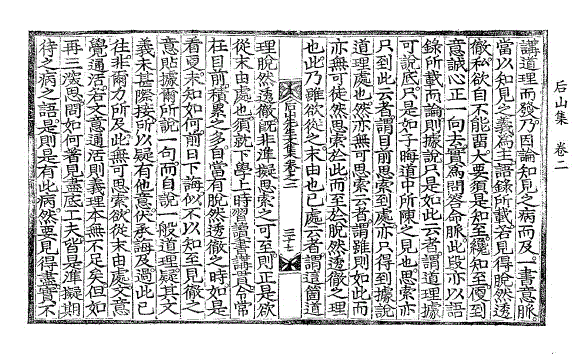 讲道理而发。乃因论知见之病而及。一书意脉。当以知见之义为主。语录所载。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实为问答命脉。此段亦以语录所载而论。则据说只是如此云者。谓道理据可说底。只是如子晦道中所陈之见也。思索亦只到此云者。谓目前思索到处。亦只得到据说道理处也。然亦无可思索云者。谓虽则如此而亦无可徒然思索于此。而至于脱然透彻之理也。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云者。谓这个道理脱然透彻。既非准拟思索之可至。则正是欲从末由处也。须就下学上时习读书讲贯。令常在目前。积累之多。自当有脱然透彻之时。如是看更。未知如何。前日下诲。似不以知至见彻之意贴据尔所说一句。而自说一般道理。疑其文义未甚际接。所以疑有他意。伏承诲及。过此已往。非尔力所及。此无可思索。欲从末由处。文意觉通活。若文意通活则义理本无不足矣。但如再三深思。问如何著见尽底工夫。皆是准拟期待之病之语。是则是有此病。然要见得尽。实不
讲道理而发。乃因论知见之病而及。一书意脉。当以知见之义为主。语录所载。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实为问答命脉。此段亦以语录所载而论。则据说只是如此云者。谓道理据可说底。只是如子晦道中所陈之见也。思索亦只到此云者。谓目前思索到处。亦只得到据说道理处也。然亦无可思索云者。谓虽则如此而亦无可徒然思索于此。而至于脱然透彻之理也。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云者。谓这个道理脱然透彻。既非准拟思索之可至。则正是欲从末由处也。须就下学上时习读书讲贯。令常在目前。积累之多。自当有脱然透彻之时。如是看更。未知如何。前日下诲。似不以知至见彻之意贴据尔所说一句。而自说一般道理。疑其文义未甚际接。所以疑有他意。伏承诲及。过此已往。非尔力所及。此无可思索。欲从末由处。文意觉通活。若文意通活则义理本无不足矣。但如再三深思。问如何著见尽底工夫。皆是准拟期待之病之语。是则是有此病。然要见得尽。实不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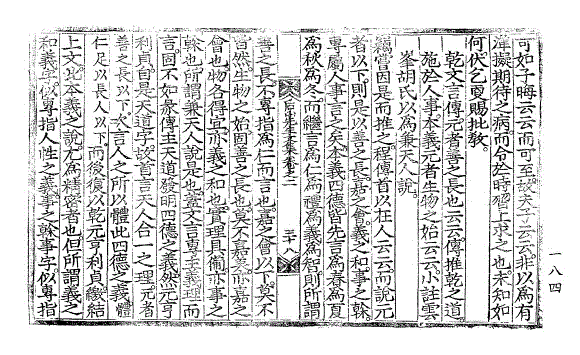 可如子晦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云云。非以为有准拟期待之病。而令于时习上求之也。未知如何。伏乞更赐批教。
可如子晦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云云。非以为有准拟期待之病。而令于时习上求之也。未知如何。伏乞更赐批教。乾文言传。元者善之长也云云。传推乾之道。施于人事。本义元者生物之始云云。小注云峰胡氏以为兼天人说。
窃尝因是而推之。程传首以在人云云。而说元者以下。则是以善之长。嘉之会。义之和。事之干。专属人事言之矣。本义四德皆先言为春为夏为秋为冬。而继言为仁为礼为义为智。则所谓善之长。不专指为仁而言也。嘉之会以下。莫不皆然。生物之始。固善之长也。莫不嘉美。亦嘉之会也。物各得宜。亦义之和也。实理具备。亦事之干也。所谓兼天人说是也。盖文言专主义理而言。固不如彖传主天道发明四德之义。然元亨利贞。自是天道字。故首言天人合一之理。(元者善之长以下。)次言人之所以体此四德之义。(体仁足以长人以下。)而后复以乾元亨利贞。缴结上文。此本义之说。尤为精密者也。但所谓义之和义字。似专指人性之义。事之干事字。似专指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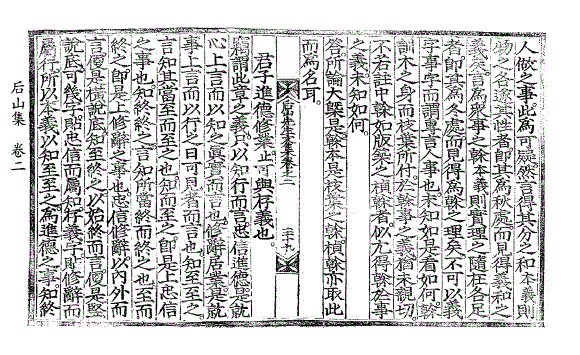 人做之事。此为可疑。然言得其分之和(本义)则物之各遂其性者。即其为秋处。而见得义和之义矣。言为众事之干(本义)则实理之随在各足者。即其为冬处。而见得为干之理矣。不可以义字事字而谓专言人事也。未知如是看如何。干训木之身而枝叶所付。于干事之义。犹未亲切。不若注中干如版筑之桢干者。似尤得干于事之义。未知如何。
人做之事。此为可疑。然言得其分之和(本义)则物之各遂其性者。即其为秋处。而见得义和之义矣。言为众事之干(本义)则实理之随在各足者。即其为冬处。而见得为干之理矣。不可以义字事字而谓专言人事也。未知如是看如何。干训木之身而枝叶所付。于干事之义。犹未亲切。不若注中干如版筑之桢干者。似尤得干于事之义。未知如何。答。所论大槩是。干本是枝叶之干。桢干亦取此而为名耳。
君子进德修业。(止)可与存义也。
窃谓此章之义。只以知行而言。忠信进德。是就心上言而以知之真实而言也。修辞居业。是就事上言而以行之日可见者而言也。知至至之。言知其当至而至之也。知而至之。即是上忠信之事也。知终终之。言知所当终而终之也。至而终之。即是上修辞之事也。忠信修辞。以内外而言。便是横说底。知至终之。以始终而言。便是竖说底。可几字。贴忠信而属知。存义字。贴修辞而属行。所以本义以知至至之。为进德之事。知终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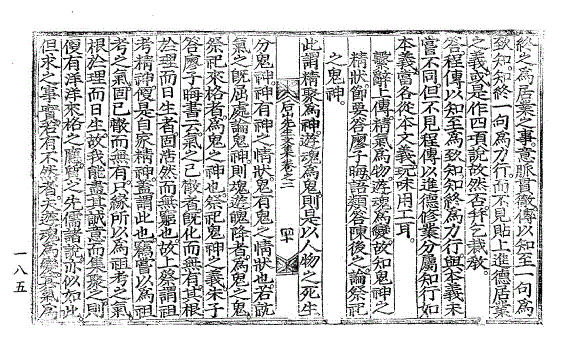 终之为居业之事。意脉贯彻。传以知至一句为致知。知终一句为力行。而不见贴上进德居业之义。或是作四项说故然否。并乞裁教。
终之为居业之事。意脉贯彻。传以知至一句为致知。知终一句为力行。而不见贴上进德居业之义。或是作四项说故然否。并乞裁教。答。程传以知至为致知。知终为力行。与本义未尝不同。但不见程传以进德修业分属知行如本义。当各从本文义。玩味用工耳。
系辞上传。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精状。节要答廖子晦。语类答陈后之。论祭祀之鬼神。
此谓精聚为神。游魂为鬼。则是以人物之死生分鬼神。神有神之情状。鬼有鬼之情状也。若就气之既屈处论鬼神。则魂游魄降者。为鬼之鬼。祭祀来格者。为鬼之神也。祭祀鬼神之义。朱子答廖子晦书云。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盖谓此也。窃尝以为祖考之气。固已散而无有。只缘所以为祖考之气。根于理而日生。故我能尽其诚意而集聚之。则便有洋洋来格之应。质之先儒诸说。亦似如此。但求之事实。若有不然者。夫游魂为变。其气为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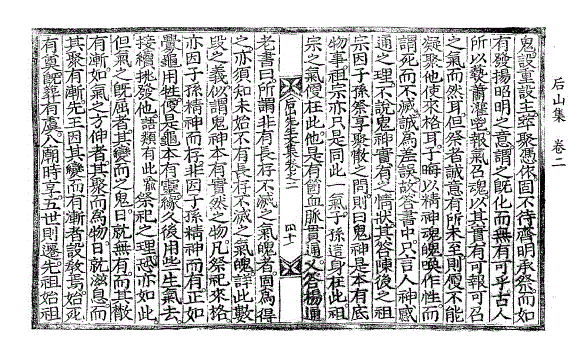 鬼。设重设主。萃聚凭依。固不待齐明承祭。而如有发扬昭明之意。谓之既化而无有可乎。古人所以爇萧灌鬯。报气召魂。以其实有可报可召之气而然耳。但祭者诚意有所未至。则便不能凝聚他使来格耳。子晦以精神魂魄唤作性。而谓死而不灭。诚为差误。故答书中。只言人神感通之理。不说鬼神实有之情状。其答陈后之祖宗因子孙祭享聚散之问。则曰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气。子孙这身在此。祖宗之气便在此。他是有个血脉贯通。又答杨通老书曰。所谓非有长存不灭之气魄者。固为得之。亦须知未始不有长存不灭之气魄。详此数段之义。似谓鬼神本有实然之物。凡祭祀来格。亦因子孙精神而存。非因子孙精神而有。正如衅龟用牲。便是龟本有灵。缘久后用些生气去。接续挑发他。(语类有此喻)祭祀之理。恐亦如此。但气之既屈者。其变而之鬼。日就无有。而其散有渐。如气之方伸者。其聚而为物。日就滋息。而其聚有渐。先王因其变而有渐者设教焉。始死有奠。既葬有虞。入庙时享。五世则迁。先祖始祖
鬼。设重设主。萃聚凭依。固不待齐明承祭。而如有发扬昭明之意。谓之既化而无有可乎。古人所以爇萧灌鬯。报气召魂。以其实有可报可召之气而然耳。但祭者诚意有所未至。则便不能凝聚他使来格耳。子晦以精神魂魄唤作性。而谓死而不灭。诚为差误。故答书中。只言人神感通之理。不说鬼神实有之情状。其答陈后之祖宗因子孙祭享聚散之问。则曰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气。子孙这身在此。祖宗之气便在此。他是有个血脉贯通。又答杨通老书曰。所谓非有长存不灭之气魄者。固为得之。亦须知未始不有长存不灭之气魄。详此数段之义。似谓鬼神本有实然之物。凡祭祀来格。亦因子孙精神而存。非因子孙精神而有。正如衅龟用牲。便是龟本有灵。缘久后用些生气去。接续挑发他。(语类有此喻)祭祀之理。恐亦如此。但气之既屈者。其变而之鬼。日就无有。而其散有渐。如气之方伸者。其聚而为物。日就滋息。而其聚有渐。先王因其变而有渐者设教焉。始死有奠。既葬有虞。入庙时享。五世则迁。先祖始祖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6L 页
 之祭。渐有等杀疏数。亦因其情状而为之制节者也。须兼前后数义看。方为该备。未知如何。其气之根于理气字。只作所以为祖考之气看。终似泛然。只把作祖考已变之气看。又似真切。如此则与陈后之以下二段。又同一语意。未知如何。伏乞开诲。
之祭。渐有等杀疏数。亦因其情状而为之制节者也。须兼前后数义看。方为该备。未知如何。其气之根于理气字。只作所以为祖考之气看。终似泛然。只把作祖考已变之气看。又似真切。如此则与陈后之以下二段。又同一语意。未知如何。伏乞开诲。答。天下之气。聚而有。散而无。人死而其气既散矣。然其散也亦有渐。而其气之传于子孙者。根于理而生生不息。故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祭祀之时。以本同一气之子孙。而致诚尽礼以求之。则彼未尽散之气。自然感格而来享。设主立庙。所以萃聚未尽散之气而欲其凭依耳。来谕根于理之气只作(止)又似真切。此一段。恐皆未安。所谓根于理者。朱子既以自家精神言之。不可直以所以为祖考之气言也。(先儒或有如此说。而恐非朱子本意。)若祖考之气则已化而无有矣。又岂有根于理而日生者耶。答陈后之问。亦与答子晦书同一语脉。恐不可差殊看也。所谓祖宗同此一气者。以下文子孙这身在此。祖宗之气便在此观之则可见矣。非谓别有沈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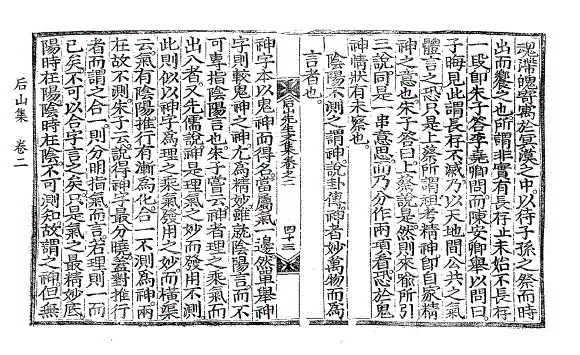 魂滞魄寄寓于冥漠之中。以待子孙之祭而时出而飨之也。所谓非实有长存(止)未始不长存一段。即朱子答李尧卿问。而陈安卿举以问曰。子晦见此谓长存不灭。乃以天地间公共之气体言之。恐只是上蔡所谓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也。朱子答曰。上蔡说是。然则来喻所引三说。同是一串意思。而乃分作两项看。恐于鬼神情状有未察也。
魂滞魄寄寓于冥漠之中。以待子孙之祭而时出而飨之也。所谓非实有长存(止)未始不长存一段。即朱子答李尧卿问。而陈安卿举以问曰。子晦见此谓长存不灭。乃以天地间公共之气体言之。恐只是上蔡所谓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也。朱子答曰。上蔡说是。然则来喻所引三说。同是一串意思。而乃分作两项看。恐于鬼神情状有未察也。阴阳不测之谓神。说卦传。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神字本以鬼神而得名。当属气一边。然单举神字则较鬼神之神。尤为精妙。虽就阴阳言。而不可专指阴阳言也。朱子尝云。神者理之乘气而出入者。又先儒说。神是理气之妙而发用不测。此则似以神字为理之乘气发用之妙。而横渠云。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两在故不测。朱子云。说得神字最分晓。盖对推行者而谓之合一。则分明指气而言。若理则一而已矣。不可以合字言之矣。只是气之最精妙底。阳时在阳。阴时在阴。不可测知。故谓之神。但无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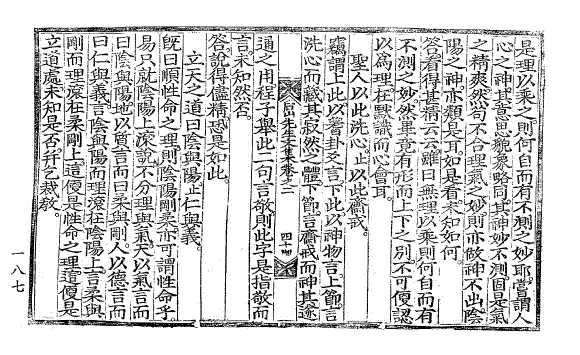 是理以乘之。则何自而有不测之妙耶。尝谓人心之神。其意思貌象略同。其神妙不测。固是气之精爽。然苟不合理气之妙。则亦做神不出。阴阳之神。亦类是耳。如是看。未知如何。
是理以乘之。则何自而有不测之妙耶。尝谓人心之神。其意思貌象略同。其神妙不测。固是气之精爽。然苟不合理气之妙。则亦做神不出。阴阳之神。亦类是耳。如是看。未知如何。答。看得甚精云云。虽曰无理以乘则何自而有不测之妙。然毕竟有形而上下之别。不可便认以为理。在默识而心会耳。
圣人以此洗心。(止)以此斋戒。
窃谓上此。以蓍卦爻言。下此。以神物言。上节。言洗心而藏其寂然之体。下节。言斋戒而神其遂通之用。程子举此二句言敬。则此字是指敬而言。未知然否。
答。说得尽精。恐是如此。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止)仁与义。
既曰顺性命之理。则阴阳刚柔。亦可谓性命乎。易只就阴阳上滚说。不分理与气。天以气言而曰阴与阳。地以质言而曰柔与刚。人以德言而曰仁与义。言阴与阳而理滚在阴阳上。言柔与刚而理滚在柔刚上。这便是性命之理。这便是立道处。未知是否。并乞裁教。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8H 页
 答。看得是。
答。看得是。上先生
雨后乍凉。伏惟静中气候对时毖卫。俞兄闻往在云洞。志气坚恳。宜其长进。甚欲图数日与闻所受。连畏热。不敢作意终一遂耳。前者下诲廖书之旨。犹有一句未会通处。宜更陈所疑。以求是正。深恐有疑即问。正犯朱门之戒。要思得无可疑而后请教。近日致思之馀。若有得于新意。谨以录其所以然者。仰备勘批。未知果能不背勤谕之旨否。兼文字间时有记疑处。以此一款未决绝。不敢杂然铺陈。容俟后耳。
别纸
向日别纸。固有一书意脉知见为主之说。而终是于亦无可思索。此乃欲从末由处。数句看不破。所以屡蒙教谕而未遽觉也。元初知解以欲从末由。为就子晦所陈道理而言。故其他语句。一向就道理上说。反与所谓知见为主之意相戾。谨悉受病之由矣。自承下诲。颇致思绎。果知前此差误处。谨复改为之说。未知又如何也。此乃云者。指见得尽而言也。欲从末由也已处云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8L 页
 者。谓欲从见得尽地位而末由也已。欲从末由一句。与无可思索一句。既一意相承。(二句下诲中语)下句指见尽地位无所用力之意。则上句之指见尽地位无所用力。亦可见矣。总而言之。如曰。若欲见尽则据说道理只是如此。思索所及亦只如此。但到此亦无可用思索者。此乃颜子所谓欲从末由也已处也。盖如此之此到此之此两此。只是一意。指子晦所陈道理而言也。此乃之此。指亦无可思索而言。即见尽地位。又与上二此。微有不同矣。大抵此书所问及语录所记。前段与此问皆说见得尽道理。故先生后答。只承问者之语而言。更不提出见尽字。直以据说如此接之。所以不见据说以下。为见得尽而言也。前书无可徒然思索。而至于脱然透彻之理一段。正欲以无可思索一句。作见得尽一边义而硬把作说。失本文之意。剖覈觉精当。下诲又谓非欲以欲从末由救无可思索之病。愚意但欲以明徒然思索于此。非所以到脱然透彻之意也。非以无可思索以下为方说病处。而以欲从末由为救病之方也。前书。不可如子晦
者。谓欲从见得尽地位而末由也已。欲从末由一句。与无可思索一句。既一意相承。(二句下诲中语)下句指见尽地位无所用力之意。则上句之指见尽地位无所用力。亦可见矣。总而言之。如曰。若欲见尽则据说道理只是如此。思索所及亦只如此。但到此亦无可用思索者。此乃颜子所谓欲从末由也已处也。盖如此之此到此之此两此。只是一意。指子晦所陈道理而言也。此乃之此。指亦无可思索而言。即见尽地位。又与上二此。微有不同矣。大抵此书所问及语录所记。前段与此问皆说见得尽道理。故先生后答。只承问者之语而言。更不提出见尽字。直以据说如此接之。所以不见据说以下。为见得尽而言也。前书无可徒然思索。而至于脱然透彻之理一段。正欲以无可思索一句。作见得尽一边义而硬把作说。失本文之意。剖覈觉精当。下诲又谓非欲以欲从末由救无可思索之病。愚意但欲以明徒然思索于此。非所以到脱然透彻之意也。非以无可思索以下为方说病处。而以欲从末由为救病之方也。前书。不可如子晦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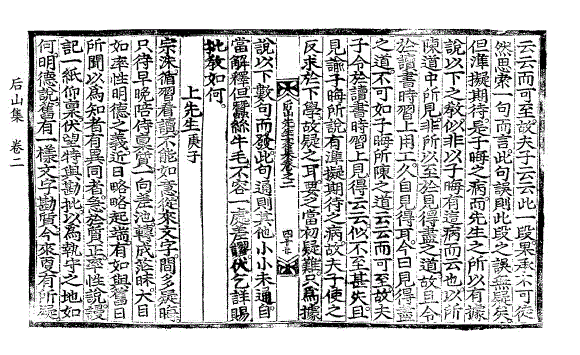 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云云此一段。果承不可徒然思索一句而言。此句误则此段之误无疑矣。但准拟期待。是子晦之病。而先生之所以有据说以下之教。似非以子晦有这病而云也。以所陈道中所见。非所以至于见得尽之道。故且令于读书时习上用工。久自见得耳。今曰见得尽之道。不可如子晦所陈之道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令于读书时习上见得云云。似不至甚失。且见谕子晦所说有准拟期待之病。故夫子使之反求于下学。故疑之耳。要之当初疑难。只为据说以下数句而发。此句通则其他小小未通。自当解释。但蚕丝牛毛。不容一处差谬。伏乞详赐批教如何。
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云云此一段。果承不可徒然思索一句而言。此句误则此段之误无疑矣。但准拟期待。是子晦之病。而先生之所以有据说以下之教。似非以子晦有这病而云也。以所陈道中所见。非所以至于见得尽之道。故且令于读书时习上用工。久自见得耳。今曰见得尽之道。不可如子晦所陈之道云云而可至。故夫子令于读书时习上见得云云。似不至甚失。且见谕子晦所说有准拟期待之病。故夫子使之反求于下学。故疑之耳。要之当初疑难。只为据说以下数句而发。此句通则其他小小未通。自当解释。但蚕丝牛毛。不容一处差谬。伏乞详赐批教如何。上先生(庚子)
宗洙。循习看读。不能如意。从来文字。间多疑晦。只待早晚陪侍禀质。一向差池。转成茫昧。大目如率性明德之义。近日略略起端。有如与旧日所闻以为知者有异同者。急于质正。率性说。谩记一纸仰禀。伏望特与勘批。以为执守之地如何。明德说。旧有一样文字勘质。今来更有所疑。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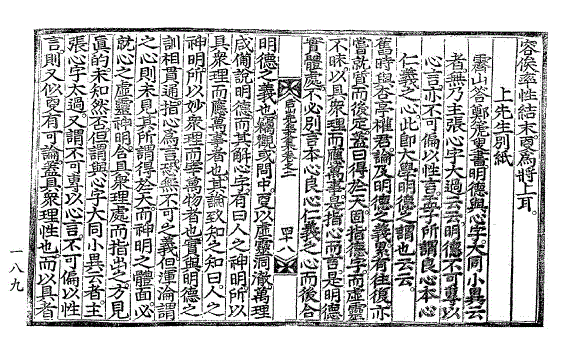 容俟率性结末。更为将上耳。
容俟率性结末。更为将上耳。上先生别纸
霁山答郑篪叟书。明德与心字。大同小异云者。无乃主张心字大过云云。明德不可专以心言。亦不可偏以性言。孟子所谓良心本心仁义之心。此即大学明德之谓也云云。
旧时与杏亭权君。论及明德之义。累有往复。亦尝就质而后定。盖曰得于天。固指德字。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是指心而言。是明德实体处。不必别言本心良心仁义之心而后合明德之义也。窃观或问中。更以虚灵洞澈。万理咸备说明德。而其解心字。有曰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其论致知之知曰。人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实与明德之训相贯通。指心为言。恐无不可之义。但浑沦谓之心则未见其所谓得于天。而神明之体面。必就心之虚灵神明。含具众理处而指出之。方见真的。未知然否。但谓与心字大同小异云者。主张心字太过。又谓不可专以心言。不可偏以性言。则又似更有可论。盖具众理性也。而以具者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90H 页
 心也。应万事情也。而以应者心也。其立言脉络。实主心而言。而性情之德备焉。谓之大同。恐不免粗说之弊。反嫌于主张心字太过。亦蒙陋所信未及处耳。若不专言心。又不偏言性。则是心与性外。又别有一部位可指言明德者。未知如何立说。免于偏倚透漏之失欤。明明德传。天之明命。分明是降衷仁义之性。格物传。吾心之全体大用。分明是明德之全体大用。一部或问中。此义间见层出。所以有不专主心。不偏言性之论。然降衷仁义之性。乃全体大用之实体。恐不须枚举而后足也。未知如何。伏乞并赐批教。
心也。应万事情也。而以应者心也。其立言脉络。实主心而言。而性情之德备焉。谓之大同。恐不免粗说之弊。反嫌于主张心字太过。亦蒙陋所信未及处耳。若不专言心。又不偏言性。则是心与性外。又别有一部位可指言明德者。未知如何立说。免于偏倚透漏之失欤。明明德传。天之明命。分明是降衷仁义之性。格物传。吾心之全体大用。分明是明德之全体大用。一部或问中。此义间见层出。所以有不专主心。不偏言性之论。然降衷仁义之性。乃全体大用之实体。恐不须枚举而后足也。未知如何。伏乞并赐批教。答先生(辛丑)
权生袖致下书。承坼不胜感豁。伏审新春。静中调候对时万福。岁除 除旨。 上恩隆重。控辞之章。留滞县道。伏惟惶惕难安。有过于前者矣。下诲谆复。敢不铭服。数年来。盖累承提耳之命。常时用力。不敢不勉于反躬一边。而未能脱然。不勇之以也。自见赋质终欠通明。凡有事来。常患理之未精。以至错做了。不能不急于求义。亦以讲闻之赐。略知义理之无穷。而觉日月迫隘。
后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1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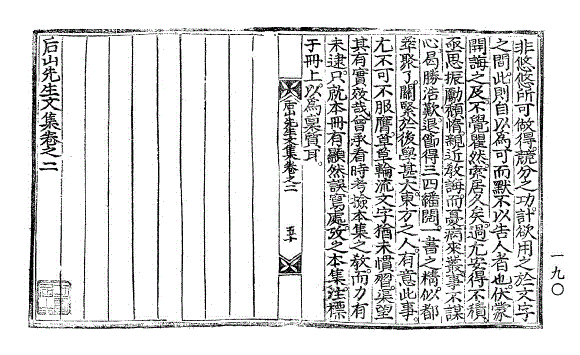 非悠悠所可做得。竞分之功。计欲用之于文字之间。此则自以为可而默不以告人者也。伏蒙开诲之及。不觉瞿然。索居久矣。过尤安得不积。亟思振励颓惰。亲近教诲。而忧病来丛。事不谋心。曷胜浩叹。退节得三四翻阅。一书之精。似都萃聚了。关紧于后学甚大。东方之人。有意此事。尤不可不服膺。草草轮流文字犹未惯习。渠望其有实效哉。曾承看时考捡本集之教。而力有未逮。只就本册有显然误写处。考之本集。注标于册上。以为禀质耳。
非悠悠所可做得。竞分之功。计欲用之于文字之间。此则自以为可而默不以告人者也。伏蒙开诲之及。不觉瞿然。索居久矣。过尤安得不积。亟思振励颓惰。亲近教诲。而忧病来丛。事不谋心。曷胜浩叹。退节得三四翻阅。一书之精。似都萃聚了。关紧于后学甚大。东方之人。有意此事。尤不可不服膺。草草轮流文字犹未惯习。渠望其有实效哉。曾承看时考捡本集之教。而力有未逮。只就本册有显然误写处。考之本集。注标于册上。以为禀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