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附录
附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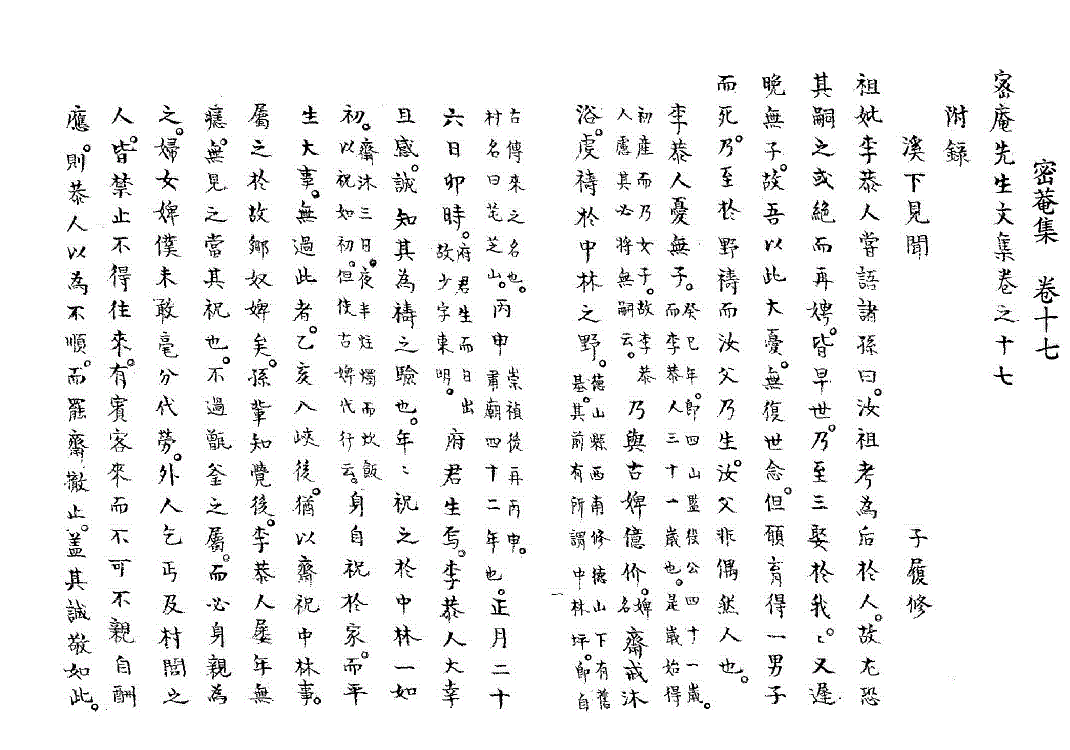 溪下见闻[子履修]
溪下见闻[子履修]祖妣李恭人尝语诸孙曰。汝祖考为后于人。故尤恐其嗣之或绝而再娉。皆早世。乃至三娶于我。我又迟晚无子。故吾以此大忧。无复世念。但愿育得一男子而死。乃至于野祷而汝父乃生。汝父非偶然人也。
李恭人忧无子。(癸巳年。即四山监役公四十一岁。而李恭人三十一岁也。是岁始得初产而乃女子。故李恭人虑其必将无嗣云。)乃与古婢亿价。(婢名)斋戒沐浴。虔祷于中林之野。(德山县西南修德山下有旧基。其前有所谓中林坪。即自古传来之名也。村名曰芚芝山。)丙申(崇祯后再丙申。 肃庙四十二年也。)正月二十六日卯时。(府君生而日出故少字东明。)府君生焉。李恭人大幸且感。诚知其为祷之验也。年年祝之于中林一如初。(斋沐三日。夜半炷烛而炊饭以祝如初。但使古婢代行云。)身自祝于家。而平生大事。无过此者。乙亥入峡后。犹以斋祝中林事。属之于故乡奴婢矣。孙辈知觉后。李恭人屡年无𤹂。无见之当其祝也。不过甑釜之属。而必身亲为之。妇女婢仆未敢毫分代劳。外人乞丐及村闾之人。皆禁止不得往来。有宾客来而不可不亲自酬应。则恭人以为不顺。而罢斋撤止。盖其诚敬如此。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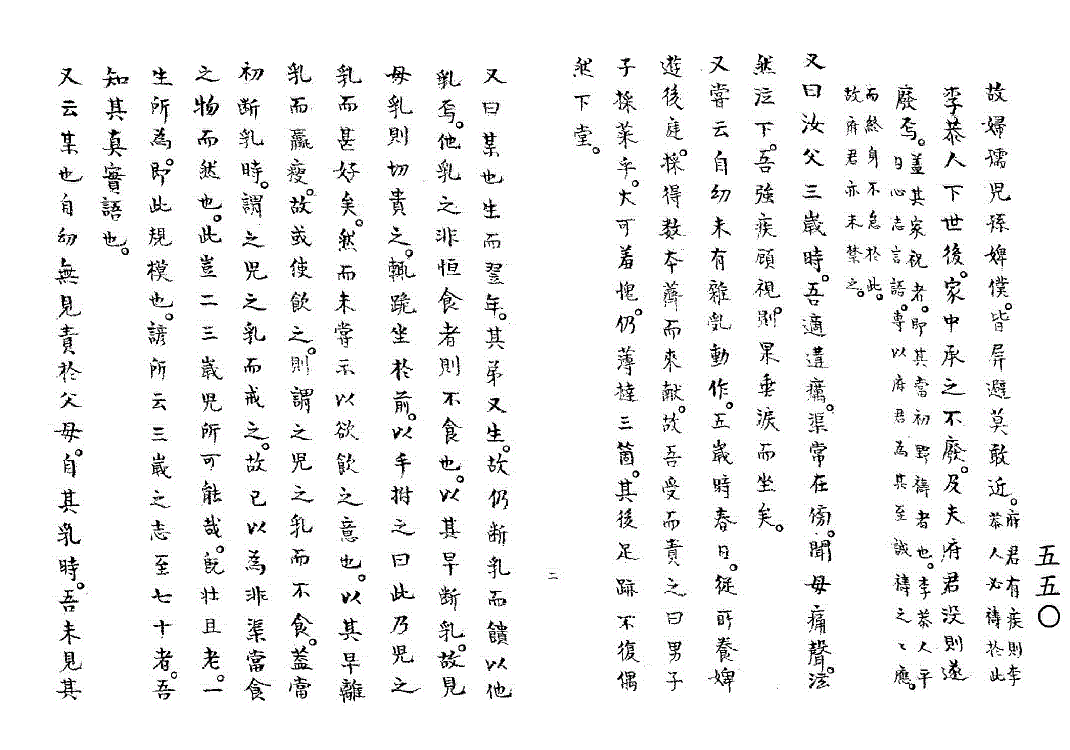 故妇孺儿孙婢仆。皆屏避莫敢近。(府君有疾则李恭人必祷于此。)李恭人下世后。家中承之不废。及夫府君没则遂废焉。(盖其家祝者。即其当初野祷者也。李恭人平日心志言语。专以府君为其至诚祷之之应。而终身不怠于此。故府君亦未禁之。)
故妇孺儿孙婢仆。皆屏避莫敢近。(府君有疾则李恭人必祷于此。)李恭人下世后。家中承之不废。及夫府君没则遂废焉。(盖其家祝者。即其当初野祷者也。李恭人平日心志言语。专以府君为其至诚祷之之应。而终身不怠于此。故府君亦未禁之。)又曰汝父三岁时。吾适遘疠。渠常在傍。闻母痛声。泫然泣下。吾强疾顾视。则果垂泪而坐矣。
又尝云自幼未有杂乱动作。五岁时春日。从所养婢游后庭。采得数本荠而来献。故吾受而责之曰男子子采菜乎。大可羞愧。仍薄挞三个。其后足迹不复偶然下堂。
又曰某也生而翌年。其弟又生。故仍断乳而馈以他乳焉。他乳之非恒食者则不食也。以其早断乳。故见母乳则切贵之。辄跪坐于前。以手拊之曰此乃儿之乳而甚好矣。然而未尝示以欲饮之意也。以其早离乳而羸瘦。故或使饮之。则谓之儿之乳而不食。盖当初断乳时。谓之儿之乳而戒之。故已以为非渠当食之物而然也。此岂二三岁儿所可能哉。既壮且老。一生所为。即此规模也。谚所云三岁之志至七十者。吾知其真实语也。
又云某也自幼无见责于父母。自其乳时。吾未见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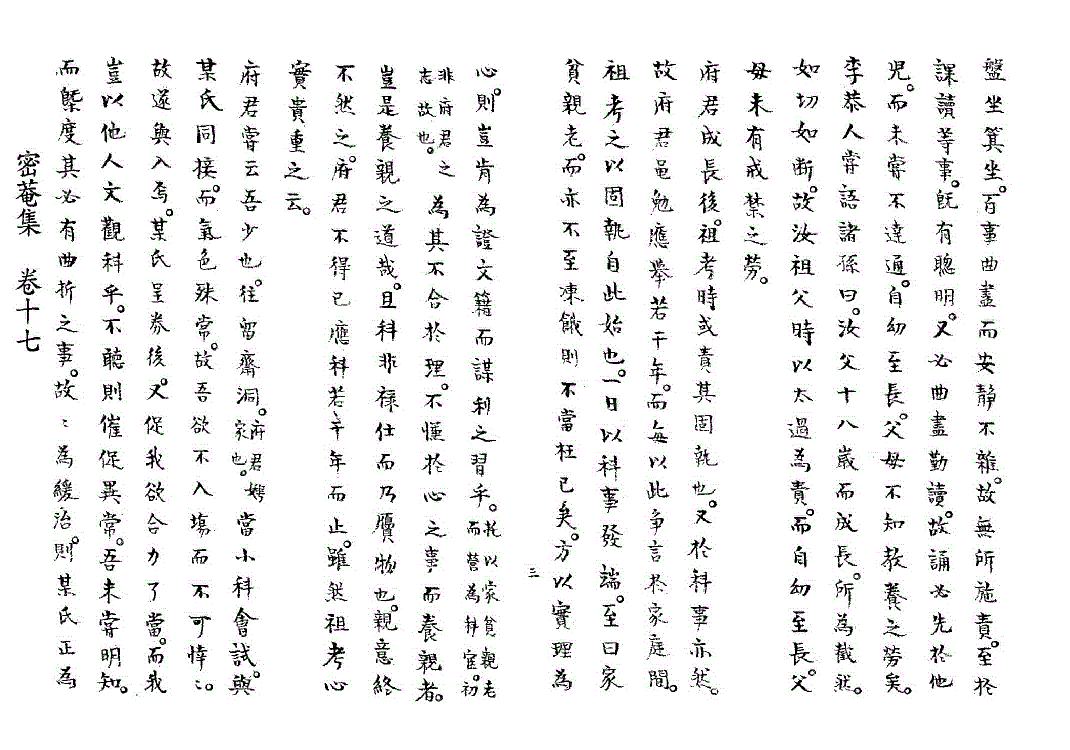 盘坐箕坐。百事曲尽而安静不杂。故无所施责。至于课读等事。既有聪明。又必曲尽勤读。故诵必先于他儿。而未尝不达通。自幼至长。父母不知教养之劳矣。李恭人尝语诸孙曰。汝父十八岁而成长。所为截然。如切如断。故汝祖父时以太过为责。而自幼至长。父母未有戒禁之劳。
盘坐箕坐。百事曲尽而安静不杂。故无所施责。至于课读等事。既有聪明。又必曲尽勤读。故诵必先于他儿。而未尝不达通。自幼至长。父母不知教养之劳矣。李恭人尝语诸孙曰。汝父十八岁而成长。所为截然。如切如断。故汝祖父时以太过为责。而自幼至长。父母未有戒禁之劳。府君成长后。祖考时或责其固执也。又于科事亦然。故府君黾勉应举若干年。而每以此争言于家庭间。祖考之以固执自此始也。一日以科事发端。至曰家贫亲老。而亦不至冻饿则不当枉己矣。方以实理为心。则岂肯为證文籍而谋利之习乎。(托以家贫亲老而营为科宦。初非府君之志故也。)为其不合于理。不慊于心之事而养亲者。岂是养亲之道哉。且科非禄仕而乃赝物也。亲意终不然之。府君不得已应科若干年而止。虽然祖考心实贵重之云。
府君尝云吾少也。往留斋洞。(府君娉家也。)当小科会试。与某氏同接。而气色殊常。故吾欲不入场而不可悻悻。故遂与入焉。某氏呈券后。又促我欲合力了当。而我岂以他人文观科乎。不听则催促异常。吾未尝明知。而槩度其必有曲折之事。故故为缓治。则某氏正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1L 页
 我憧憧焦燥。吾强坐至昏。仍不呈券而出也。其后复以对疑发解。与同志(再从某氏。于府君同年而少月日。)赴会试。疑题义有分岐。故与之论难。此非但本心不欲弥缝呈券也。又方以讲义便作大事。忘却日暮。仍以不必呈券作计。讲尽其义而出也。其后不复应举。
我憧憧焦燥。吾强坐至昏。仍不呈券而出也。其后复以对疑发解。与同志(再从某氏。于府君同年而少月日。)赴会试。疑题义有分岐。故与之论难。此非但本心不欲弥缝呈券也。又方以讲义便作大事。忘却日暮。仍以不必呈券作计。讲尽其义而出也。其后不复应举。又云与某氏同接时事追思之。犹觉汗出沾背。心必惊眩。若临渊谷而免者。其后亦屡言曰。与某氏仝接时事。至今思之。不觉汗背矣。其科试官搜吾试券而不得之说闻之。正觉神奇。吾所不呈而出者。终是天诱也。吾之有为。系关天运。则决无不自作而遽堕其中之理而然也。
府君气像。表里洞彻。人之初面者。未必亲熟而便无隔膜。故使人不自觉其心无间而言尽情也。
府君尝语不肖曰。读论语最好。沦肌浃髓。如诵己言。则一生须用不尽。
又尝语曰人毋或自有。毋或口给。自有则哲人不谋。口给则正义自蔽。哲谟不来。日缩之道也。正理不明。不乱何为。书曰自用则小。又曰罔以辨言。此非但人君之事。自天子达于庶人。府君尝云道是日用而流行者。自其知者观之。则实无隐奥难见。即其物事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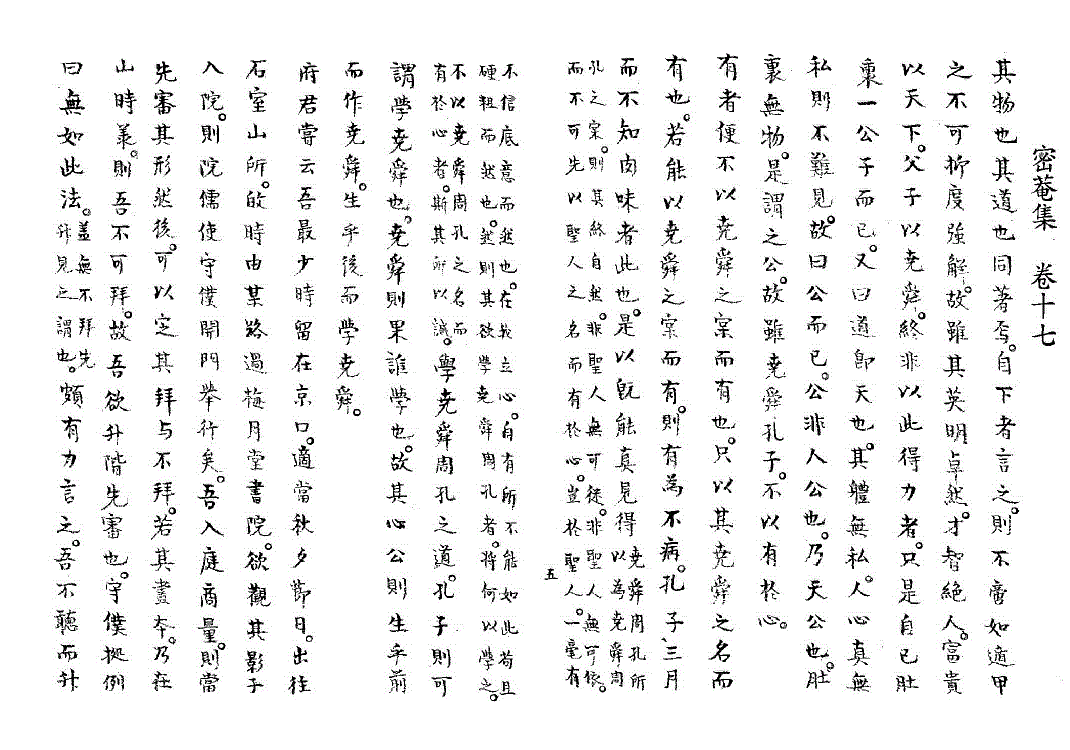 其物也其道也同著焉。自下者言之。则不啻如遁甲之不可抑度强解。故虽其英明卓然。才智绝人。富贵以天下。父子以尧舜。终非以此得力者。只是自己肚里一公子而已。又曰道即天也。其体无私。人心真无私则不难见。故曰公而已。公非人公也。乃天公也。肚里无物。是谓之公。故虽尧舜孔子。不以有于心。
其物也其道也同著焉。自下者言之。则不啻如遁甲之不可抑度强解。故虽其英明卓然。才智绝人。富贵以天下。父子以尧舜。终非以此得力者。只是自己肚里一公子而已。又曰道即天也。其体无私。人心真无私则不难见。故曰公而已。公非人公也。乃天公也。肚里无物。是谓之公。故虽尧舜孔子。不以有于心。有者便不以尧舜之宲而有也。只以其尧舜之名而有也。若能以尧舜之宲而有。则有为不病。孔子三月而不知肉味者此也。是以既能真见得(尧舜周孔所以为尧舜周孔之宲。则其终自然。非圣人无可从。非圣人无可依。而不可先以圣人之名而有于心。岂于圣人。一毫有不信底意而然也。在我立心。自有所不能如此苟且硬粗而然也。然则其欲学尧舜周孔者。将何以学之。不以尧舜周孔之名而有于心者。斯其所以诚。)学尧舜周孔之道。孔子则可谓学尧舜也。尧舜则果谁学也。故其心公则生乎前而作尧舜。生乎后而学尧舜。
府君尝云吾最少时留在京口。适当秋夕节日。出往石室山所。敀时由某路过梅月堂书院。欲观其影子入院。则院儒使守仆开门举行矣。吾入庭商量。则当先审其形然后。可以定其拜与不拜。若其画本。乃在山时羕。则吾不可拜。故吾欲升阶先审也。守仆据例曰无如此法。(盖无不拜先升见之谓也。)颇有力言之。吾不听而升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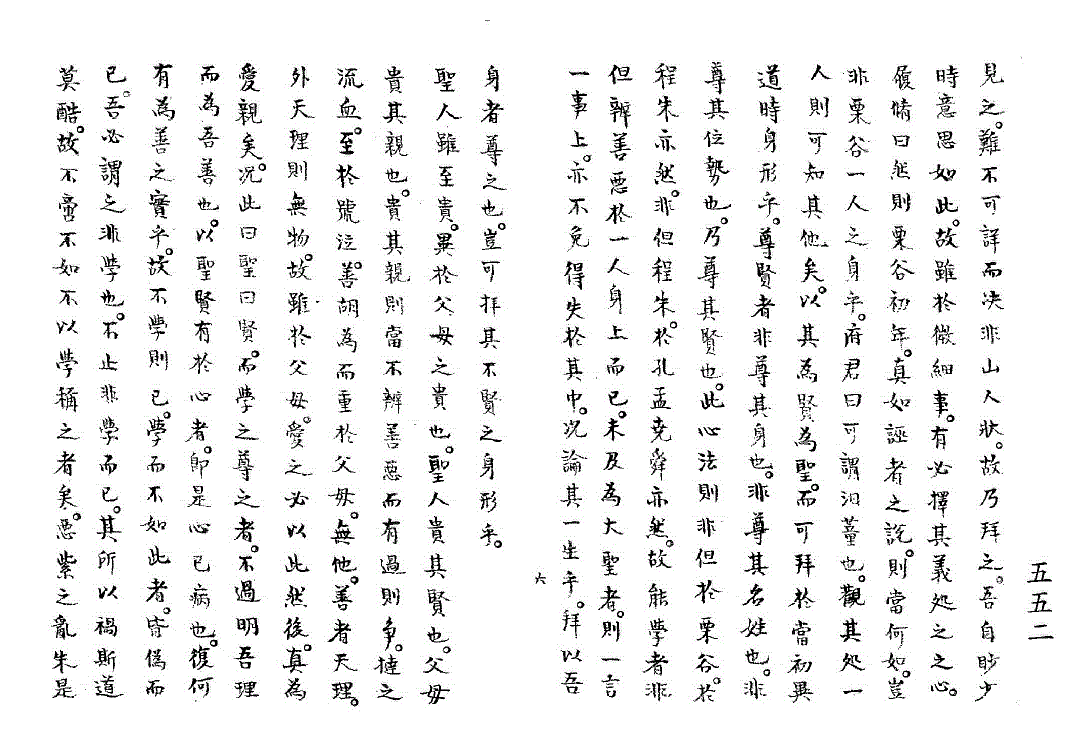 见之。难不可详而决非山人状。故乃拜之。吾自眇少时意思如此。故虽于微细事。有必择其义处之之心。履脩曰然则栗谷初年。真如诬者之说。则当何如。岂非栗谷一人之身乎。府君曰可谓汩蕫也。观其处一人则可知其他矣。以其为贤为圣。而可拜于当初异道时身形乎。尊贤者非尊其身也。非尊其名姓也。非尊其位势也。乃尊其贤也。此心法则非但于栗谷。于程朱亦然。非但程朱。于孔孟尧舜亦然。故能学者非但辨善恶于一人身上而已。未及为大圣者。则一言一事上。亦不免得失于其中。况论其一生乎。拜以吾身者尊之也。岂可拜其不贤之身形乎。
见之。难不可详而决非山人状。故乃拜之。吾自眇少时意思如此。故虽于微细事。有必择其义处之之心。履脩曰然则栗谷初年。真如诬者之说。则当何如。岂非栗谷一人之身乎。府君曰可谓汩蕫也。观其处一人则可知其他矣。以其为贤为圣。而可拜于当初异道时身形乎。尊贤者非尊其身也。非尊其名姓也。非尊其位势也。乃尊其贤也。此心法则非但于栗谷。于程朱亦然。非但程朱。于孔孟尧舜亦然。故能学者非但辨善恶于一人身上而已。未及为大圣者。则一言一事上。亦不免得失于其中。况论其一生乎。拜以吾身者尊之也。岂可拜其不贤之身形乎。圣人虽至贵。异于父母之贵也。圣人贵其贤也。父母贵其亲也。贵其亲则当不辨善恶而有过则争。挞之流血。至于号泣。善胡为而重于父母。无他。善者天理。外天理则无物。故虽于父母。爱之必以此然后。真为爱亲矣。况此曰圣曰贤。而学之尊之者。不过明吾理而为吾善也。以圣贤有于心者。即是心已病也。复何有为善之实乎。故不学则已。学而不如此者。皆伪而已。吾必谓之非学也。不止非学而已。其所以祸斯道莫酷。故不啻不如不以学称之者矣。恶紫之乱朱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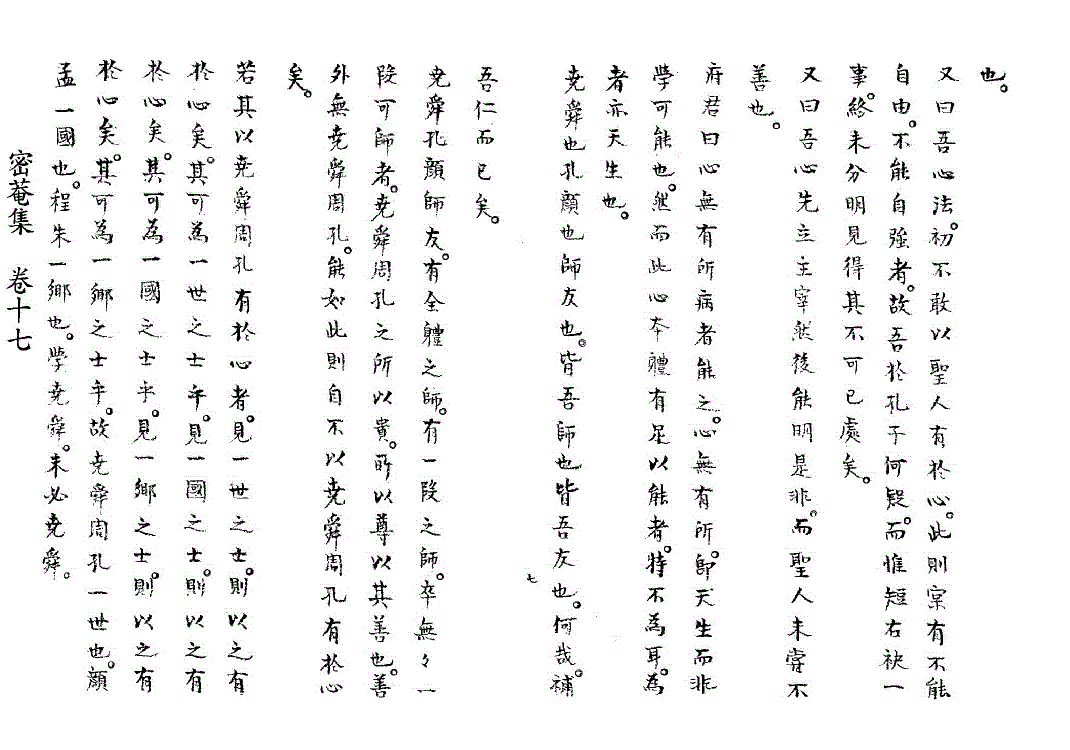 也。
也。又曰吾心法。初不敢以圣人有于心。此则宲有不能自由。不能自强者。故吾于孔子何疑。而惟短右袂一事。终未分明见得其不可已处矣。
又曰吾心先立主宰然后能明是非。而圣人未尝不善也。
府君曰心无有所病者能之。心无有所。即天生而非学可能也。然而此心本体有足以能者。特不为耳。为者亦天生也。
尧舜也孔颜也师友也。皆吾师也皆吾友也。何哉。补吾仁而已矣。
尧舜孔颜师友。有全体之师。有一段之师。卒无无一段可师者。尧舜周孔之所以贵。所以尊以其善也。善外无尧舜周孔。能如此则自不以尧舜周孔有于心矣。
若其以尧舜周孔有于心者。见一世之士。则以之有于心矣。其可为一世之士乎。见一国之士。则以之有于心矣。其可为一国之士乎。见一乡之士。则以之有于心矣。其可为一乡之士乎。故尧舜周孔一世也。颜孟一国也。程朱一乡也。学尧舜。未必尧舜。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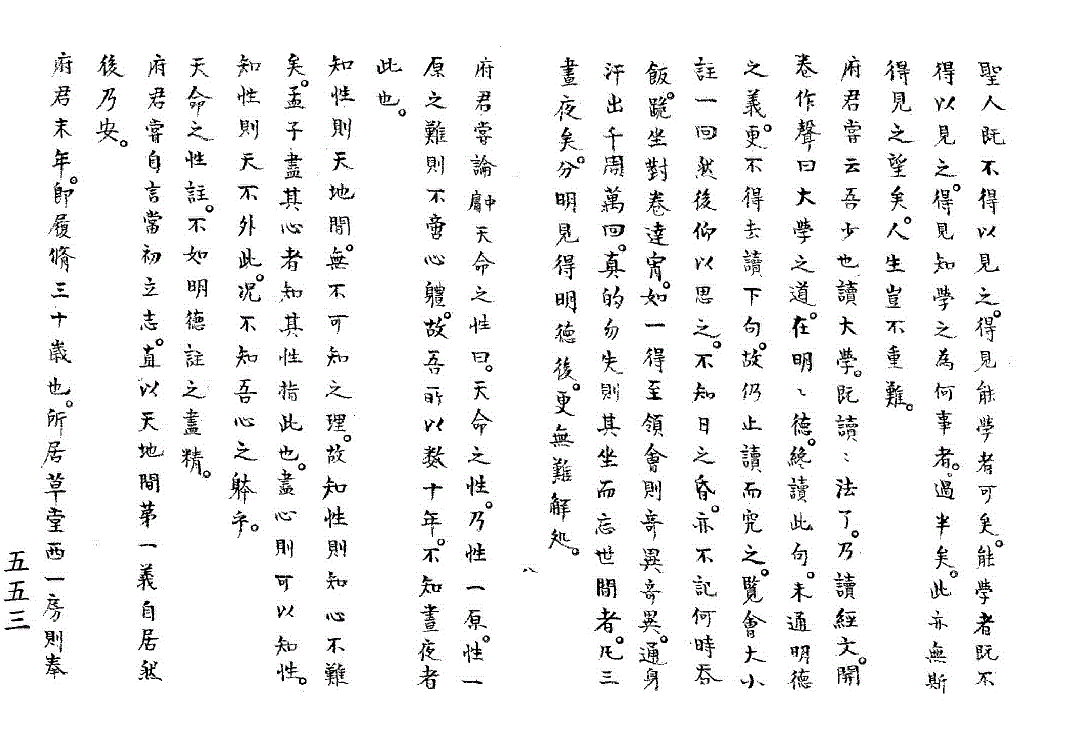 圣人既不得以见之。得见能学者可矣。能学者既不得以见之。得见知学之为何事者。斯过半矣。此亦无得见之望矣。人生岂不重难。
圣人既不得以见之。得见能学者可矣。能学者既不得以见之。得见知学之为何事者。斯过半矣。此亦无得见之望矣。人生岂不重难。府君尝云吾少也读大学。既读读法了。乃读经文。开卷作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才读此句。未通明德之义。更不得去读下句。故仍止读而究之。览会大小注一回然后仰以思之。不知日之昏。亦不记何时吞饭。跪坐对卷达宵。如一得至领会则奇异奇异。通身汗出千周万回。真的勿失则其坐而忘世间者。凡三昼夜矣。分明见得明德后。更无难解处。
府君尝论(中庸)天命之性曰。天命之性。乃性一原。性一原之难则不啻心体。故吾所以数十年。不知昼夜者此也。
知性则天地间。无不可知之理。故知性则知心不难矣。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指此也。尽心则可以知性。知性则天不外此。况不知吾心之体乎。
天命之性注。不如明德注之尽精。
府君尝自言当初立志。直以天地间第一义自居然后乃安。
府君末年。即履脩三十岁也。所居草堂西一房则奉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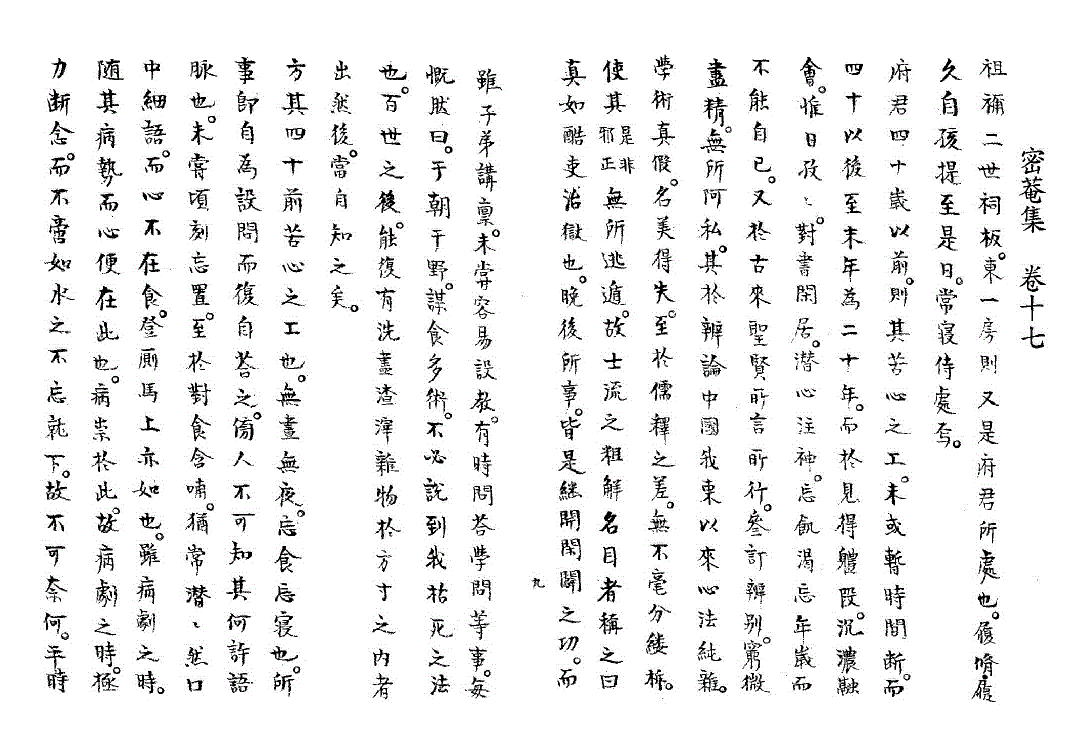 祖祢二世祠板。东一房则又是府君所处也。履脩,履久自孩提至是日。常寝侍处焉。
祖祢二世祠板。东一房则又是府君所处也。履脩,履久自孩提至是日。常寝侍处焉。府君四十岁以前。则其苦心之工。未或暂时间断。而四十以后至末年为二十年。而于见得体段。沉浓融会。惟日孜孜。对书闲居。潜心注神。忘饥渴忘年岁而不能自已。又于古来圣贤所言所行。参订辨别。穷微尽精。无所阿私。其于辨论中国我东以来心法纯杂。学术真假。名美得失。至于儒释之差。无不毫分缕析。使其(是非邪正)无所逃遁。故士流之粗解名目者称之曰真如酷吏治狱也。晚后所事。皆是继开闲辟之功。而虽子弟讲禀。未尝容易设教。有时问答学问等事。每慨然曰。于朝于野。谋食多术。不必说到我枯死之法也。百世之后。能复有洗尽渣滓杂物于方寸之内者出然后。当自知之矣。
方其四十前苦心之工也。无昼无夜。忘食忘寝也。所事即自为设问而复自答之。傍人不可知其何许语脉也。未尝顷刻忘置。至于对食含哺。犹常潜潜然口中细语。而心不在食。登厕马上亦如也。虽病剧之时。随其病势而心便在此也。病祟于此。故病剧之时。极力断念。而不啻如水之不忘就下。故不可奈何。平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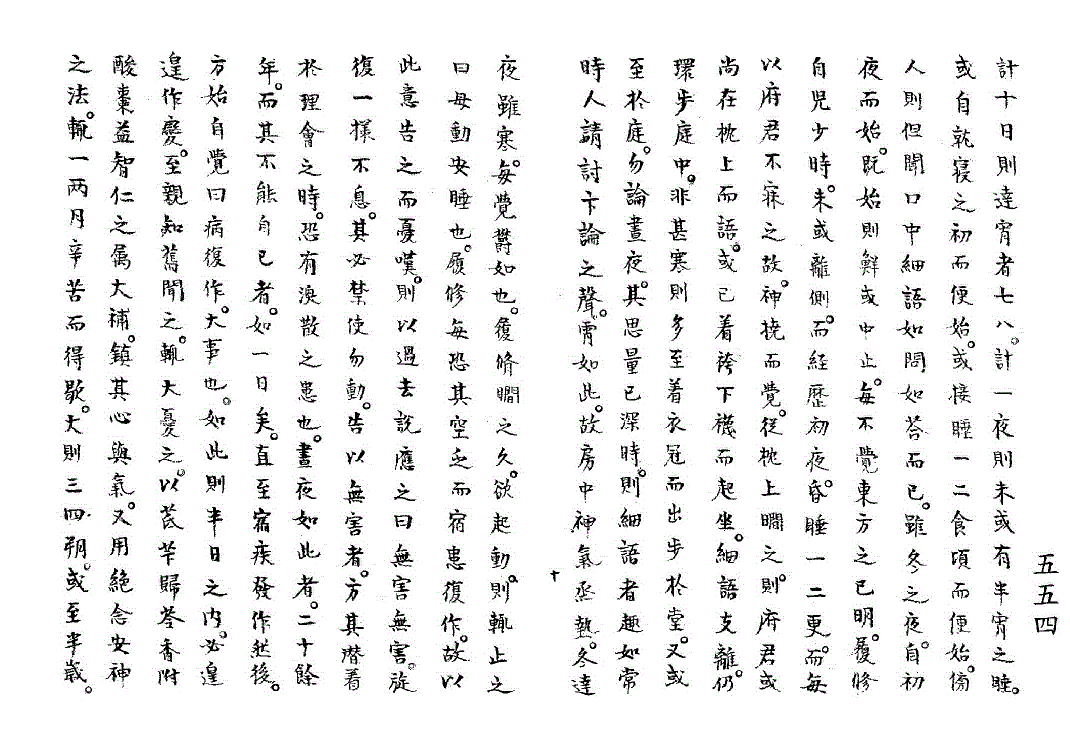 计十日则达宵者七八。计一夜则未或有半宵之睡。或自就寝之初而便始。或接睡一二食顷而便始。傍人则但闻口中细语如问如答而已。虽冬之夜。自初夜而始。既始则鲜或中止。每不觉东方之已明。履修自儿少时。未或离侧。而经历初夜。昏睡一二更。而每以府君不寐之故。神挠而觉。从枕上𣊺(一作瞷)之。则府君或尚在枕上而语。或已着裤下袜而起坐。细语支离。仍环步庭中。非甚寒则多至着衣冠而出步于堂。又或至于庭。勿论昼夜。其思量已深时。则细语者趣如常时人请讨卞论之声。宵如此。故房中神气烝热。冬达夜虽寒。每觉郁如也。履脩瞷之久。欲起动。则辄止之曰毋动安睡也。履修每恐其空乏而宿患复作。故以此意告之而忧叹。则以过去说应之曰无害无害。旋复一㨾不息。其必禁使勿动。告以无害者。方其潜着于理会之时。恐有涣散之患也。昼夜如此者。二十馀年。而其不能自已者。如一日矣。直至宿疾发作然后。方始自觉曰病复作。大事也。如此则半日之内。必遑遑作变。至亲知旧闻之。辄大忧之。以菧苄归苓香附酸枣益智仁之属大补。镇其心与气。又用绝念安神之法。辄一两月辛苦而得歇。大则三四朔。或至半岁。
计十日则达宵者七八。计一夜则未或有半宵之睡。或自就寝之初而便始。或接睡一二食顷而便始。傍人则但闻口中细语如问如答而已。虽冬之夜。自初夜而始。既始则鲜或中止。每不觉东方之已明。履修自儿少时。未或离侧。而经历初夜。昏睡一二更。而每以府君不寐之故。神挠而觉。从枕上𣊺(一作瞷)之。则府君或尚在枕上而语。或已着裤下袜而起坐。细语支离。仍环步庭中。非甚寒则多至着衣冠而出步于堂。又或至于庭。勿论昼夜。其思量已深时。则细语者趣如常时人请讨卞论之声。宵如此。故房中神气烝热。冬达夜虽寒。每觉郁如也。履脩瞷之久。欲起动。则辄止之曰毋动安睡也。履修每恐其空乏而宿患复作。故以此意告之而忧叹。则以过去说应之曰无害无害。旋复一㨾不息。其必禁使勿动。告以无害者。方其潜着于理会之时。恐有涣散之患也。昼夜如此者。二十馀年。而其不能自已者。如一日矣。直至宿疾发作然后。方始自觉曰病复作。大事也。如此则半日之内。必遑遑作变。至亲知旧闻之。辄大忧之。以菧苄归苓香附酸枣益智仁之属大补。镇其心与气。又用绝念安神之法。辄一两月辛苦而得歇。大则三四朔。或至半岁。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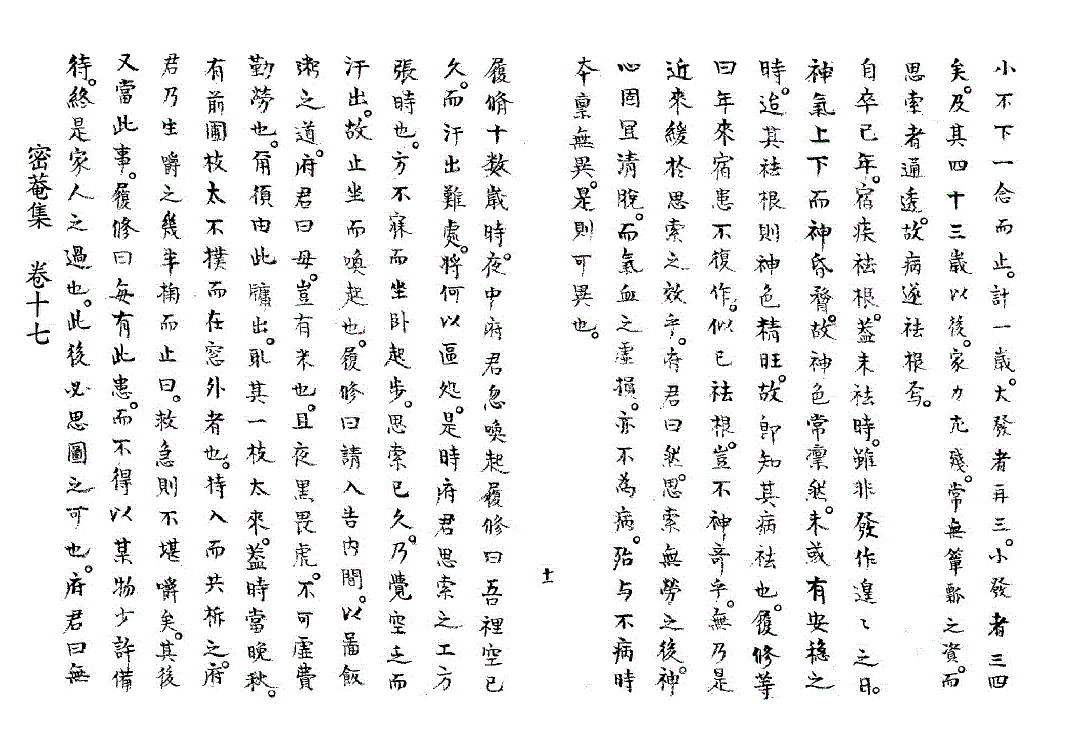 小不下一念而止。计一岁。大发者再三。小发者三四矣。及其四十三岁以后。家力尤残。常无箪瓢之资。而思索者通透。故病遂祛根焉。
小不下一念而止。计一岁。大发者再三。小发者三四矣。及其四十三岁以后。家力尤残。常无箪瓢之资。而思索者通透。故病遂祛根焉。自卒已年。宿疾祛根。盖未祛时。虽非发作遑遑之日。神气上下而神昏瞀。故神色常凛然。未或有安稳之时。迨其祛根则神色精旺。故即知其病祛也。履修等曰年来宿患不复作。似已祛根。岂不神奇乎。无乃是近来缓于思索之效乎。府君曰然。思索无劳之后。神心固宜清脱。而气血之虚损。亦不为病。殆与不病时本禀无异。是则可异也。
履脩十数岁时。夜中府君忽唤起履修曰吾里空已久。而汗出难处。将何以区处。是时府君思素之工方张时也。方不寐而坐卧起步。思索已久。乃觉空乏而汗出。故止坐而唤起也。履修曰请入告内间。以啚饭粥之道。府君曰毋。岂有米也。且夜黑畏虎。不可虚费勤劳也。尔须由此牖出。取其一枝太来。盖时当晚秋。有前圃枝太不扑而在窗外者也。持入而共析之。府君乃生嚼之几半掬而止曰。救急则不堪嚼矣。其后又当此事。履修曰每有此患。而不得以某物少许备待。终是家人之过也。此后必思图之可也。府君曰无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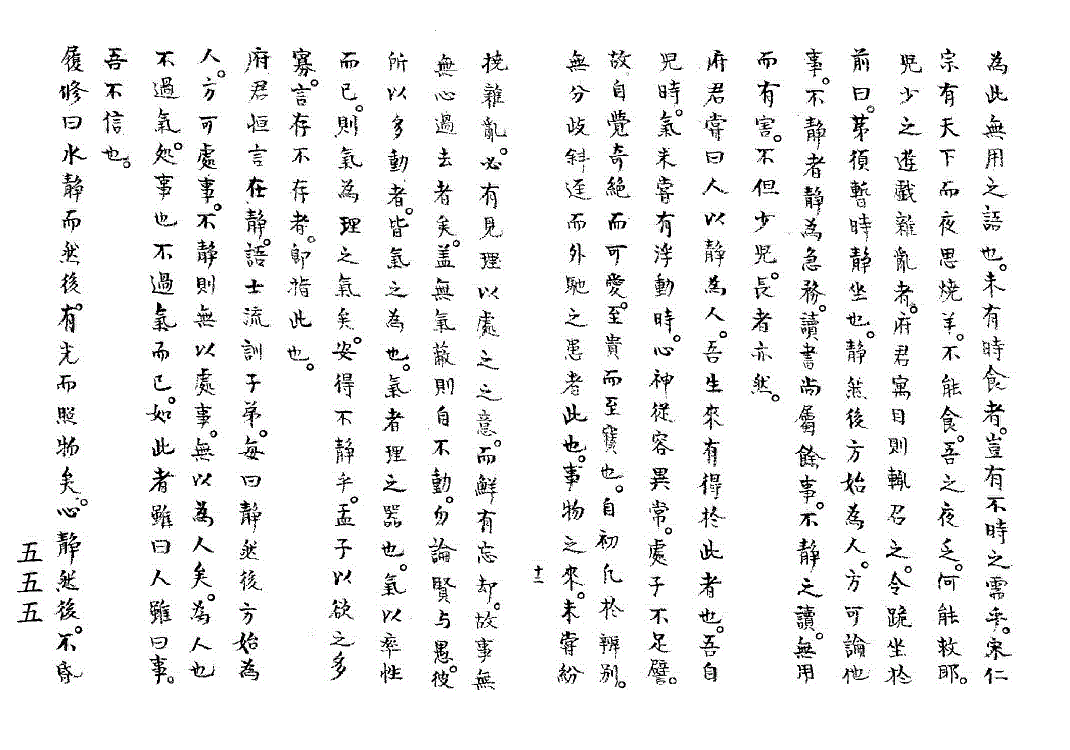 为此无用之语也。未有时食者。岂有不时之需乎。宋仁宗有天下而夜思烧羊。不能食。吾之夜乏。何能救耶。儿少之游戏杂乱者。府君寓目则辄召之。令跪坐于前曰。第须暂时静坐也。静然后方始为人。方可论他事。不静者静为急务。读书尚属馀事。不静之读。无用而有害。不但少儿。长者亦然。
为此无用之语也。未有时食者。岂有不时之需乎。宋仁宗有天下而夜思烧羊。不能食。吾之夜乏。何能救耶。儿少之游戏杂乱者。府君寓目则辄召之。令跪坐于前曰。第须暂时静坐也。静然后方始为人。方可论他事。不静者静为急务。读书尚属馀事。不静之读。无用而有害。不但少儿。长者亦然。府君尝曰人以静为人。吾生来有得于此者也。吾自儿时。气未尝有浮动时。心神从容异常。处子不足譬。故自觉奇绝而可爱。至贵而至宝也。自初凡于辨别。无分歧斜径而外驰之患者此也。事物之来。未尝纷挠杂乱。必有见理以处之之意。而鲜有忘却。故事无无心过去者矣。盖无气蔽则自不动。勿论贤与愚。彼所以多动者。皆气之为也。气者理之器也。气以率性而已。则气为理之气矣。安得不静乎。孟子以欲之多寡。言存不存者。即指此也。
府君恒言在静。语士流训子弟。每曰静然后方始为人。方可处事。不静则无以处事。无以为人矣。为人也不过气。处事也不过气而已。如此者虽曰人虽曰事。吾不信也。
履修曰水静而然后。有光而照物矣。心静然后。不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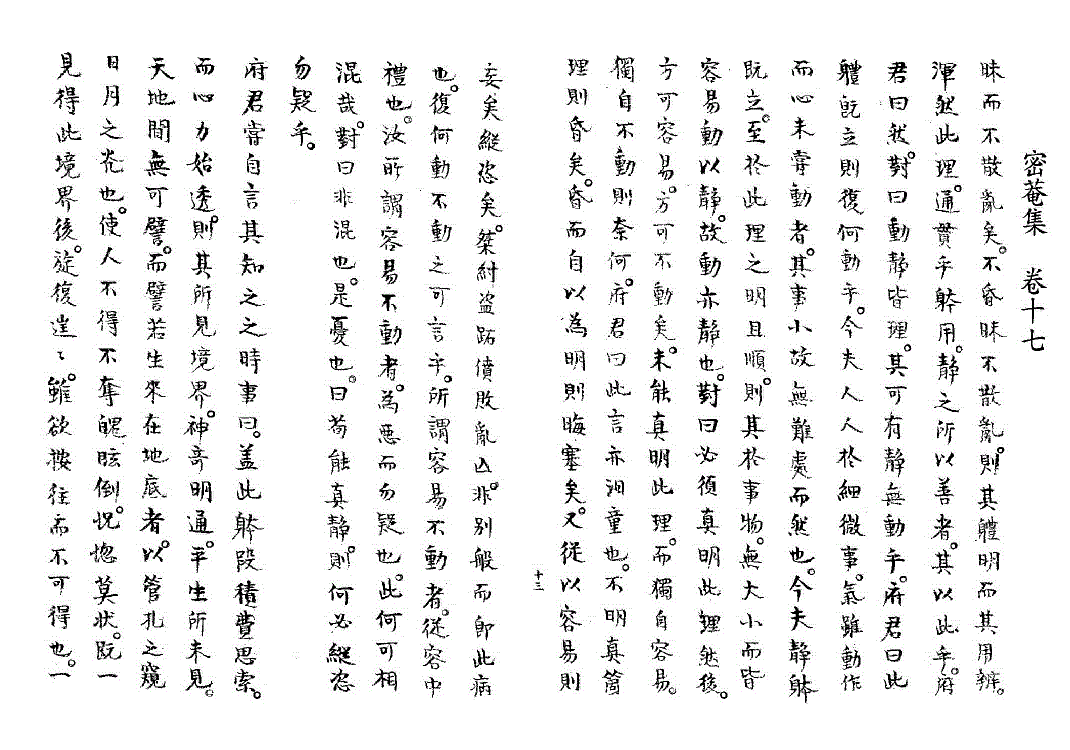 昧而不散乱矣。不昏昧不散乱。则其体明而其用辨。浑然此理。通贯乎体用。静之所以善者。其以此乎。府君曰然。对曰动静皆理。其可有静无动乎。府君曰此体既立则复何动乎。今夫人人于细微事。气虽动作而心未尝动者。其事小故无难处而然也。今夫静体既立。至于此理之明且顺。则其于事物。无大小而皆容易动以静。故动亦静也。对曰必须真明此理然后。方可容易。方可不动矣。未能真明此理。而独自容易。独自不动则奈何。府君曰此言亦汩童也。不明真个理则昏矣。昏而自以为明则晦塞矣。又从以容易则妄矣纵恣矣。桀纣盗蹠偾败乱亡。非别般而即此病也。复何动不动之可言乎。所谓容易不动者。从容中礼也。汝所谓容易不动者。为恶而勿疑也。此何可相混哉。对曰非混也。是忧也。曰苟能真静。则何必纵恣勿疑乎。
昧而不散乱矣。不昏昧不散乱。则其体明而其用辨。浑然此理。通贯乎体用。静之所以善者。其以此乎。府君曰然。对曰动静皆理。其可有静无动乎。府君曰此体既立则复何动乎。今夫人人于细微事。气虽动作而心未尝动者。其事小故无难处而然也。今夫静体既立。至于此理之明且顺。则其于事物。无大小而皆容易动以静。故动亦静也。对曰必须真明此理然后。方可容易。方可不动矣。未能真明此理。而独自容易。独自不动则奈何。府君曰此言亦汩童也。不明真个理则昏矣。昏而自以为明则晦塞矣。又从以容易则妄矣纵恣矣。桀纣盗蹠偾败乱亡。非别般而即此病也。复何动不动之可言乎。所谓容易不动者。从容中礼也。汝所谓容易不动者。为恶而勿疑也。此何可相混哉。对曰非混也。是忧也。曰苟能真静。则何必纵恣勿疑乎。府君尝自言其知之之时事曰。盖此体段积费思索。而心力始透。则其所见境界。神奇明通。平生所未见。天地间无可譬。而譬若生来在地底者。以管孔之窥日月之光也。使人不得不夺魄眩倒。恍惚莫状。既一见得此境界后。旋复𨓏𨓏。虽欲按往而不可得也。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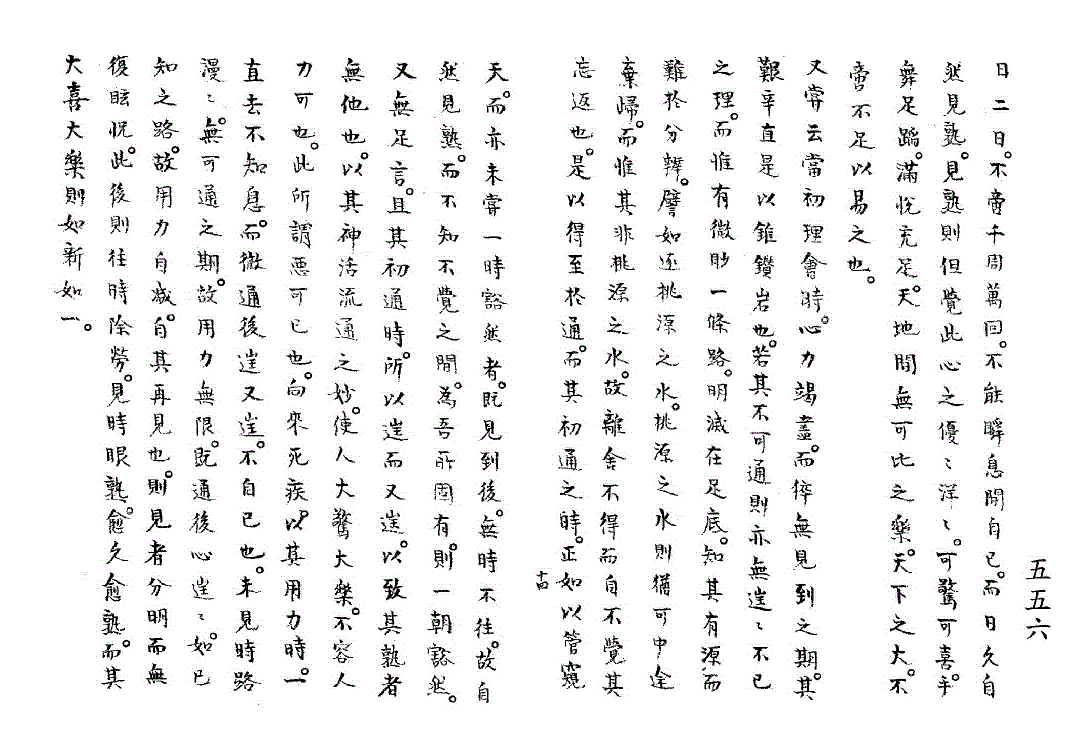 日二日。不啻千周万回。不能瞬息间自已。而日久自然见熟。见熟则但觉此心之优优洋洋。可惊可喜。手舞足蹈。满悦充足。天地间无可比之乐。天下之大。不啻不足以易之也。
日二日。不啻千周万回。不能瞬息间自已。而日久自然见熟。见熟则但觉此心之优优洋洋。可惊可喜。手舞足蹈。满悦充足。天地间无可比之乐。天下之大。不啻不足以易之也。又尝云当初理会时。心力竭尽。而猝无见到之期。其艰辛直是以锥钻岩也。若其不可通则亦无𨓏𨓏不已之理。而惟有微眇一条路。明灭在足底。知其有源而难于分辨。譬如逐桃源之水。桃源之水则犹可中途弃归。而惟其非挑源之水。故离舍不得而自不觉其忘返也。是以得至于通。而其初通之时。正如以管窥天。而亦未尝一时豁然者。既见到后。无时不往。故自然见熟。而不知不觉之间。为吾所固有。则一朝豁然。又无足言。且其初通时。所以𨓏而又𨓏。以致其熟者无他也。以其神活流通之妙。使人大惊大乐。不容人力可也。此所谓恶可已也。向来死疾。以其用力时。一直去不知息。而微通后𨓏又𨓏。不自已也。未见时路漫漫。无可通之期。故用力无限。既通后心𨓏𨓏。如已知之路。故用力自减。自其再见也。则见者分明而无复眩恍。此后则往时除劳。见时眼熟。愈久愈熟。而其大喜大乐则如新如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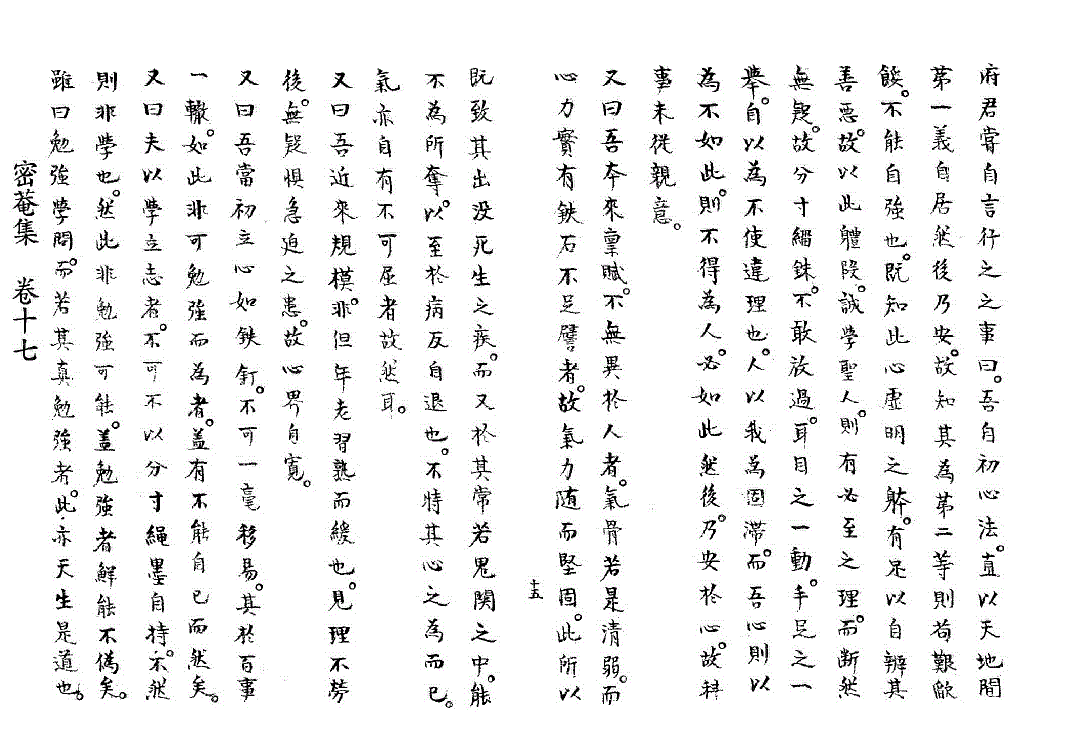 府君尝自言行之之事曰。吾自初心法。直以天地间第一义自居然后乃安。故知其为第二等则苟艰欿馁。不能自强也。既知此心虚明之体。有足以自辨其善恶。故以此体段。诚学圣人。则有必至之理。而断然无疑。故分寸缁铢。不敢放过。耳目之一动。手足之一举。自以为不使违理也。人以我为固滞。而吾心则以为不如此。则不得为人。必如此然后。乃安于心。故科事未从亲意。
府君尝自言行之之事曰。吾自初心法。直以天地间第一义自居然后乃安。故知其为第二等则苟艰欿馁。不能自强也。既知此心虚明之体。有足以自辨其善恶。故以此体段。诚学圣人。则有必至之理。而断然无疑。故分寸缁铢。不敢放过。耳目之一动。手足之一举。自以为不使违理也。人以我为固滞。而吾心则以为不如此。则不得为人。必如此然后。乃安于心。故科事未从亲意。又曰吾本来禀赋。不无异于人者。气骨若是清弱。而心力实有铁石不足譬者。故气力随而坚固。此所以既致其出没死生之疾。而又于其常若鬼关之中。能不为所夺。以至于病反自退也。不特其心之为而已。气亦自有不可屈者故然耳。
又曰吾近来规模。非但年老习熟而缓也。见理不劳后。无疑惧急迫之患。故心界自宽。
又曰吾当初立心如铁钉。不可一毫移易。其于百事一辙。如此非可勉强而为者。盖有不能自已而然矣。又曰夫以学立志者。不可不以分寸绳墨自持。不然则非学也。然此非勉强可能。盖勉强者鲜能不伪矣。虽曰勉强学问。而若其真勉强者。此亦天生是道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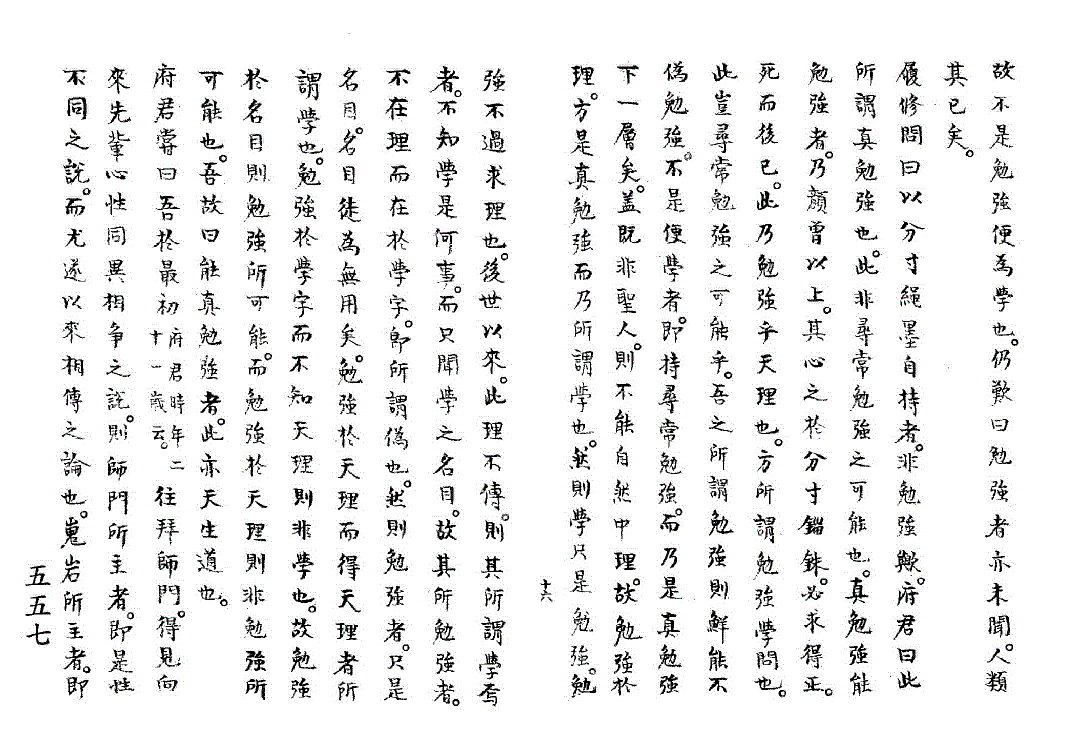 故不是勉强便为学也。仍叹曰勉强者亦未闻。人类其已矣。
故不是勉强便为学也。仍叹曰勉强者亦未闻。人类其已矣。履修问曰以分寸绳墨自持者。非勉强欤。府君曰此所谓真勉强也。此非寻常勉强之可能也。真勉强能勉强者。乃颜曾以上。其心之于分寸锱铢。必求得正。死而后已。此乃勉强乎天理也。方所谓勉强学问也。此岂寻常勉强之可能乎。吾之所谓勉强则鲜能不伪勉强。不是便学者。即持寻常勉强。而乃是真勉强下一层矣。盖既非圣人。则不能自然中理。故勉强于理。方是真勉强而乃所谓学也。然则学只是勉强。勉强不过求理也。后世以来。此理不传。则其所谓学焉者。不知学是何事。而只闻学之名目。故其所勉强者。不在理而在于学字。即所谓伪也。然则勉强者。只是名目。名目徒为无用矣。勉强于天理而得天理者所谓学也。勉强于学字而不知天理则非学也。故勉强于名目则勉强所可能。而勉强于天理则非勉强所可能也。吾故曰能真勉强者。此亦天生道也。
府君尝曰吾于最初(府君时年二十一岁云。)往拜师门。得见向来先辈心性同异相争之说。则师门所主者。即是性不同之说。而尤,遂以来相传之论也。嵬岩所主者。即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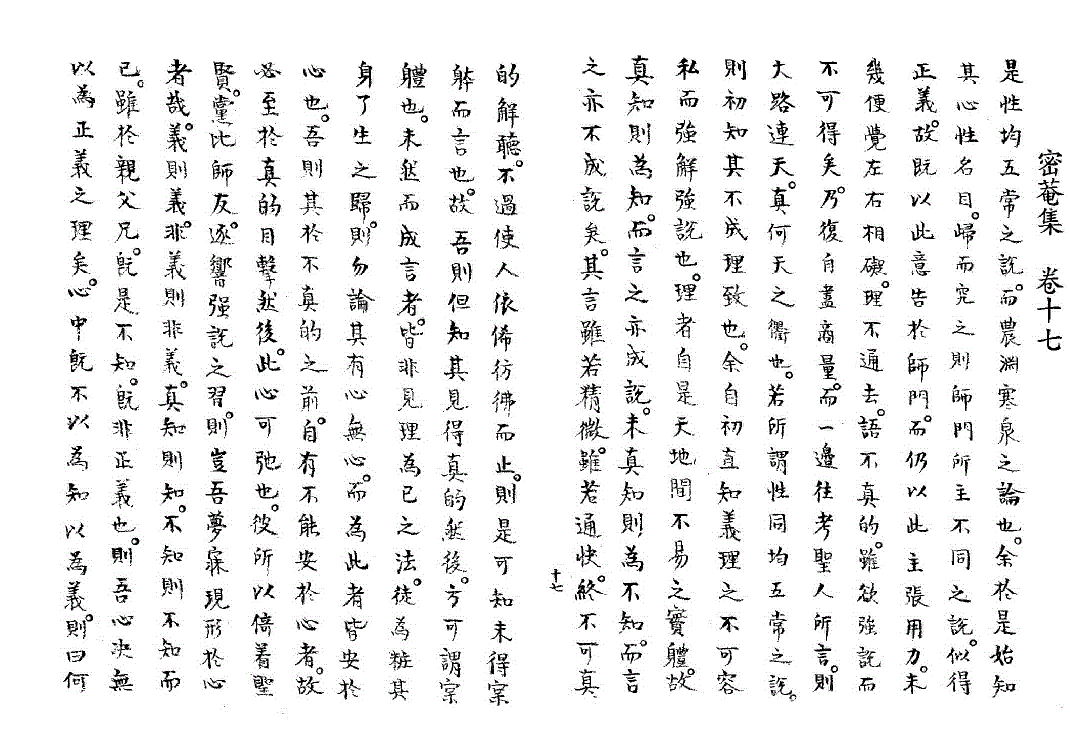 是性均五常之说。而农,渊,寒泉之论也。余于是始知其心性名目。归而究之则师门所主不同之说。似得正义。故既以此意告于师门。而仍以此主张用力。未几便觉左右相碍。理不通去。语不真的。虽欲强说而不可得矣。乃复自尽商量。而一边往考圣人所言。则大路连天。真何天之衢也。若所谓性同均五常之说。则初知其不成理致也。余自初直知义理之不可容私而强解强说也。理者自是天地间不易之实体。故真知则为知。而言之亦成说。未真知则为不知。而言之亦不成说矣。其言虽若精微。虽若通快。终不可真的解听。不过使人依俙彷佛而止。则是可知未得宲体而言也。故吾则但知其见得真的然后。方可谓宲体也。未然而成言者。皆非见理为己之法。从为妆其身了生之归。则勿论其有心无心。而为此者皆安于心也。吾则其于不真的之前。自有不能安于心者。故必至于真的目击然后。此心可弛也。彼所以倚着圣贤。党比师友。逐响强说之习。则岂吾梦寐现形于心者哉。义则义。非义则非义。真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而已。虽于亲父兄。既是不知。既非正义也。则吾心决无以为正义之理矣。心中既不以为知以为义。则曰何
是性均五常之说。而农,渊,寒泉之论也。余于是始知其心性名目。归而究之则师门所主不同之说。似得正义。故既以此意告于师门。而仍以此主张用力。未几便觉左右相碍。理不通去。语不真的。虽欲强说而不可得矣。乃复自尽商量。而一边往考圣人所言。则大路连天。真何天之衢也。若所谓性同均五常之说。则初知其不成理致也。余自初直知义理之不可容私而强解强说也。理者自是天地间不易之实体。故真知则为知。而言之亦成说。未真知则为不知。而言之亦不成说矣。其言虽若精微。虽若通快。终不可真的解听。不过使人依俙彷佛而止。则是可知未得宲体而言也。故吾则但知其见得真的然后。方可谓宲体也。未然而成言者。皆非见理为己之法。从为妆其身了生之归。则勿论其有心无心。而为此者皆安于心也。吾则其于不真的之前。自有不能安于心者。故必至于真的目击然后。此心可弛也。彼所以倚着圣贤。党比师友。逐响强说之习。则岂吾梦寐现形于心者哉。义则义。非义则非义。真知则知。不知则不知而已。虽于亲父兄。既是不知。既非正义也。则吾心决无以为正义之理矣。心中既不以为知以为义。则曰何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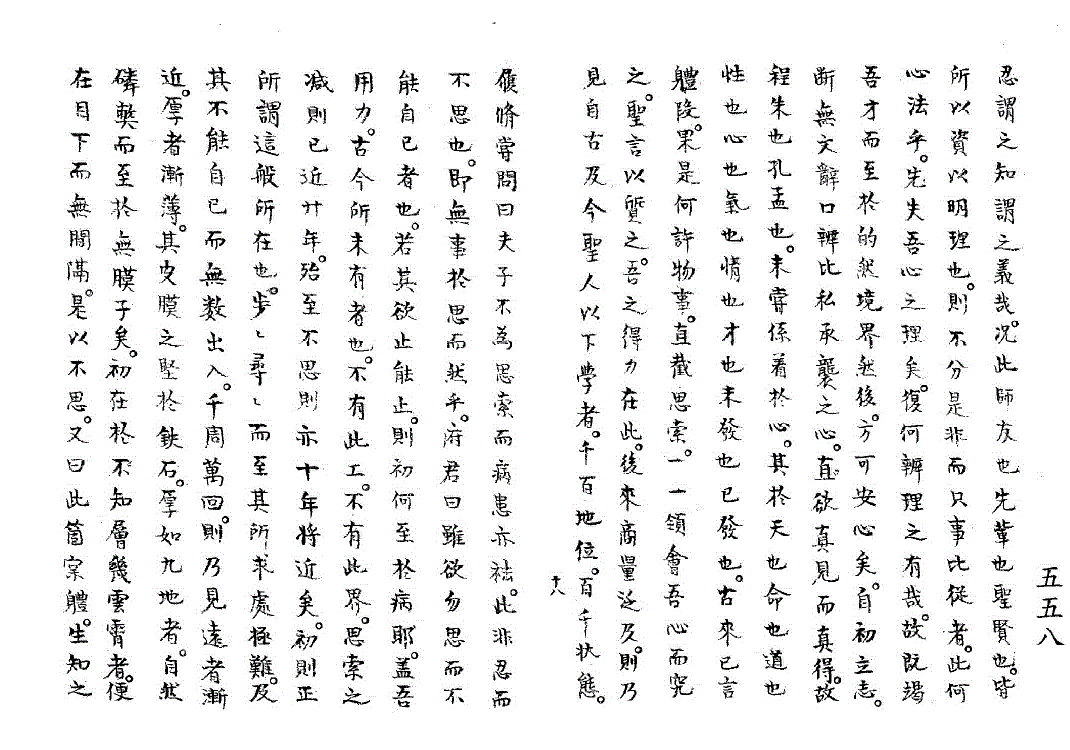 忍谓之知谓之义哉。况此师友也先辈也圣贤也。皆所以资以明理也。则不分是非而只事比从者。此何心法乎。先失吾心之理矣。复何辨理之有哉。故既竭吾才而至于的然境界然后。方可安心矣。自初立志。断无文辞口辨比私承袭之心。故直欲真见而真得。程朱也孔孟也。未尝系着于心。其于天也命也道也性也心也气也情也才也未发也已发也。古来已言体段。果是何许物事。直截思索。一一领会吾心而究之。圣言以质之。吾之得力在此。后来商量泛及。则乃见自古及今圣人以下学者。千百地位。百千状态。
忍谓之知谓之义哉。况此师友也先辈也圣贤也。皆所以资以明理也。则不分是非而只事比从者。此何心法乎。先失吾心之理矣。复何辨理之有哉。故既竭吾才而至于的然境界然后。方可安心矣。自初立志。断无文辞口辨比私承袭之心。故直欲真见而真得。程朱也孔孟也。未尝系着于心。其于天也命也道也性也心也气也情也才也未发也已发也。古来已言体段。果是何许物事。直截思索。一一领会吾心而究之。圣言以质之。吾之得力在此。后来商量泛及。则乃见自古及今圣人以下学者。千百地位。百千状态。履脩尝问曰夫子不为思索而病患亦祛。此非忍而不思也。即无事于思而然乎。府君曰虽欲勿思而不能自已者也。若其欲止能止。则初何至于病耶。盖吾用力。古今所未有者也。不有此工。不有此界。思索之减则已近廿年。殆至不思则亦十年将近矣。初则正所谓这般所在也。步步寻寻而至其所求处极难。及其不能自已而无数出入。千周万回。则乃见远者渐近。厚者渐薄。其皮膜之坚于铁石。厚如九地者。自然磷弊而至于无膜子矣。初在于不知层几云霄者。便在目下而无间隔。是以不思。又曰此个宲体。生知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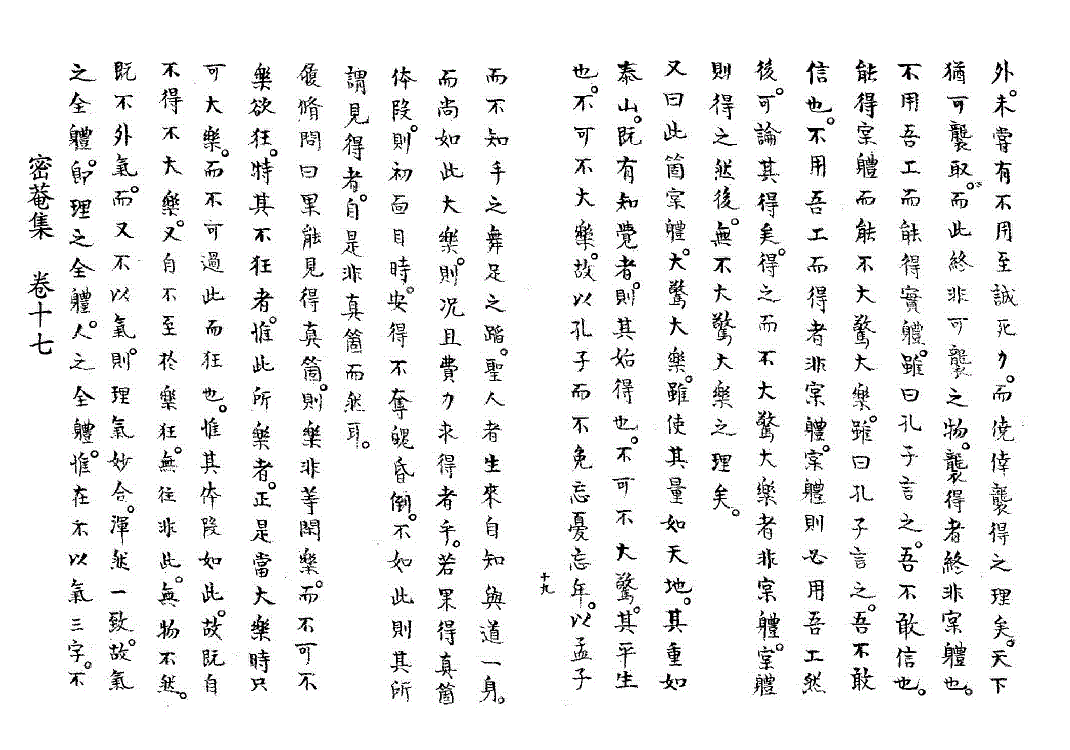 外。未尝有不用至诚死力。而侥倖袭得之理矣。天下犹可袭取。而此终非可袭之物。袭得者终非宲体也。不用吾工而能得实体。虽曰孔子言之。吾不敢信也。能得宲体而能不大惊大乐。虽曰孔子言之。吾不敢信也。不用吾工而得者非宲体。宲体则必用吾工然后。可论其得矣。得之而不大惊大乐者非宲体。宲体则得之然后。无不大惊大乐之理矣。
外。未尝有不用至诚死力。而侥倖袭得之理矣。天下犹可袭取。而此终非可袭之物。袭得者终非宲体也。不用吾工而能得实体。虽曰孔子言之。吾不敢信也。能得宲体而能不大惊大乐。虽曰孔子言之。吾不敢信也。不用吾工而得者非宲体。宲体则必用吾工然后。可论其得矣。得之而不大惊大乐者非宲体。宲体则得之然后。无不大惊大乐之理矣。又曰此个宲体。大惊大乐。虽使其量如天地。其重如泰山。既有知觉者。则其始得也。不可不大惊。其平生也。不可不大乐。故以孔子而不免忘忧忘年。以孟子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圣人者生来自知与道一身。而尚如此大乐。则况且费力求得者乎。若果得真个体段。则初面目时。安得不夺魄昏倒。不如此则其所谓见得者。自是非真个而然耳。
履脩问曰果能见得真个。则乐非等闲乐。而不可不乐欲狂。特其不狂者。惟此所乐者。正是当大乐时只可大乐。而不可过此而狂也。惟其体段如此。故既自不得不大乐。又自不至于乐狂。无往非此。无物不然。既不外气。而又不以气。则理气妙合。浑然一致。故气之全体。即理之全体。人之全体。惟在不以气三字。不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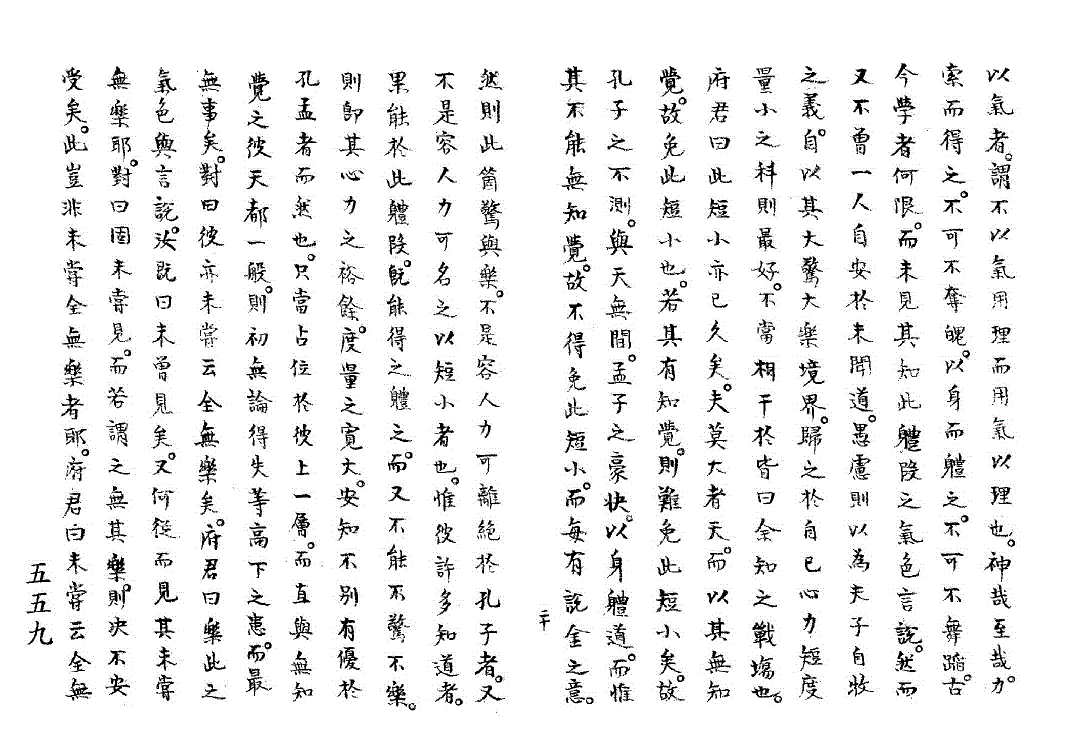 以气者。谓不以气用理而用气以理也。神哉至哉。力索而得之。不可不夺魄。以身而体之。不可不舞蹈。古今学者何限。而未见其知此体段之气色言说。然而又不曾一人自安于未闻道。愚虑则以为夫子自牧之义。自以其大惊大乐境界。归之于自己心力短度量小之科则最好。不当相干于皆曰余知之战场也。府君曰此短小亦已久矣。夫莫大者天。而以其无知觉。故免此短小也。若其有知觉。则难免此短小矣。故孔子之不测。与天无间。孟子之豪快。以身体道。而惟其不能无知觉。故不得免此短小。而每有说金之意。然则此个惊与乐。不是容人力可离绝于孔子者。又不是容人力可名之以短小者也。惟彼许多知道者。果能于此体段。既能得之体之。而又不能不惊不乐。则即其心力之裕馀。度量之宽大。安知不别有优于孔孟者而然也。只当占位于彼上一层。而直与无知觉之彼天都一般。则初无论得失等高下之患。而最无事矣。对曰彼亦未尝云全无乐矣。府君曰乐此之气色与言说。汝既曰未曾见矣。又何从而见其未尝无乐耶。对曰固未尝见。而若谓之无其乐。则决不安受矣。此岂非未尝全无乐者耶。府君白未尝云全无
以气者。谓不以气用理而用气以理也。神哉至哉。力索而得之。不可不夺魄。以身而体之。不可不舞蹈。古今学者何限。而未见其知此体段之气色言说。然而又不曾一人自安于未闻道。愚虑则以为夫子自牧之义。自以其大惊大乐境界。归之于自己心力短度量小之科则最好。不当相干于皆曰余知之战场也。府君曰此短小亦已久矣。夫莫大者天。而以其无知觉。故免此短小也。若其有知觉。则难免此短小矣。故孔子之不测。与天无间。孟子之豪快。以身体道。而惟其不能无知觉。故不得免此短小。而每有说金之意。然则此个惊与乐。不是容人力可离绝于孔子者。又不是容人力可名之以短小者也。惟彼许多知道者。果能于此体段。既能得之体之。而又不能不惊不乐。则即其心力之裕馀。度量之宽大。安知不别有优于孔孟者而然也。只当占位于彼上一层。而直与无知觉之彼天都一般。则初无论得失等高下之患。而最无事矣。对曰彼亦未尝云全无乐矣。府君曰乐此之气色与言说。汝既曰未曾见矣。又何从而见其未尝无乐耶。对曰固未尝见。而若谓之无其乐。则决不安受矣。此岂非未尝全无乐者耶。府君白未尝云全无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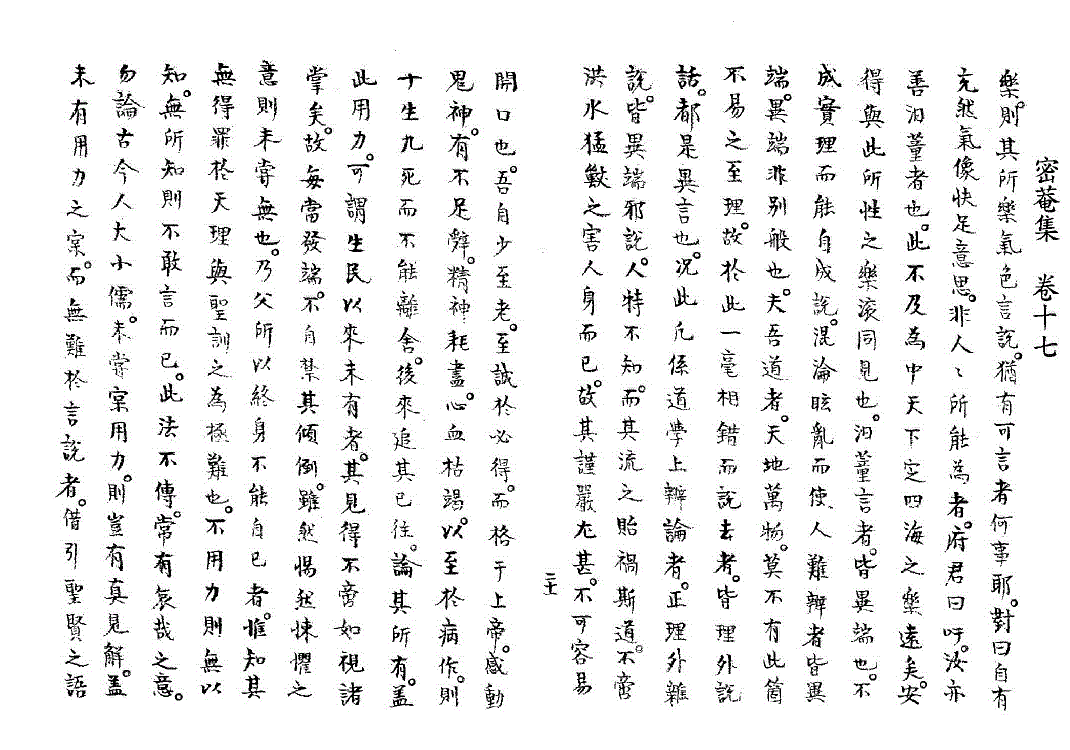 乐。则其所乐气色言说。犹有可言者何事耶。对曰自有充然气像快足意思。非人人所能为者。府君曰吁。汝亦善汩蕫者也。此不及为中天下定四海之乐远矣。安得与此所性之乐滚同见也。汩蕫言者。皆异端也。不成实理而能自成说。混沦眩乱而使人难辨者皆异端。异端非别般也。夫吾道者。天地万物。莫不有此个不易之至理。故于此一毫相错而说去者。皆理外说话。都是异言也。况此凡系道学上辨论者。正理外杂说。皆异端邪说。人特不知。而其流之贻祸斯道。不啻洪水猛兽之害人身而已。故其谨严尤甚。不可容易开口也。吾自少至老。至诚于必得。而格于上帝。感动鬼神。有不足辞。精神耗尽。心血枯竭。以至于病作。则十生九死而不能离舍。后来追其已往。论其所有。盖此用力。可谓生民以来未有者。其见得不啻如视诸掌矣。故每当发端。不自禁其倾倒。虽然惕然悚惧之意则未尝无也。乃父所以终身不能自已者。惟知其无得罪于天理与圣训之为极难也。不用力则无以知。无所知则不敢言而已。此法不传。常有哀哉之意。勿论古今人大小儒。未尝宲用力。则岂有真见解。盖未有用力之宲。而无难于言说者。借引圣贤之语
乐。则其所乐气色言说。犹有可言者何事耶。对曰自有充然气像快足意思。非人人所能为者。府君曰吁。汝亦善汩蕫者也。此不及为中天下定四海之乐远矣。安得与此所性之乐滚同见也。汩蕫言者。皆异端也。不成实理而能自成说。混沦眩乱而使人难辨者皆异端。异端非别般也。夫吾道者。天地万物。莫不有此个不易之至理。故于此一毫相错而说去者。皆理外说话。都是异言也。况此凡系道学上辨论者。正理外杂说。皆异端邪说。人特不知。而其流之贻祸斯道。不啻洪水猛兽之害人身而已。故其谨严尤甚。不可容易开口也。吾自少至老。至诚于必得。而格于上帝。感动鬼神。有不足辞。精神耗尽。心血枯竭。以至于病作。则十生九死而不能离舍。后来追其已往。论其所有。盖此用力。可谓生民以来未有者。其见得不啻如视诸掌矣。故每当发端。不自禁其倾倒。虽然惕然悚惧之意则未尝无也。乃父所以终身不能自已者。惟知其无得罪于天理与圣训之为极难也。不用力则无以知。无所知则不敢言而已。此法不传。常有哀哉之意。勿论古今人大小儒。未尝宲用力。则岂有真见解。盖未有用力之宲。而无难于言说者。借引圣贤之语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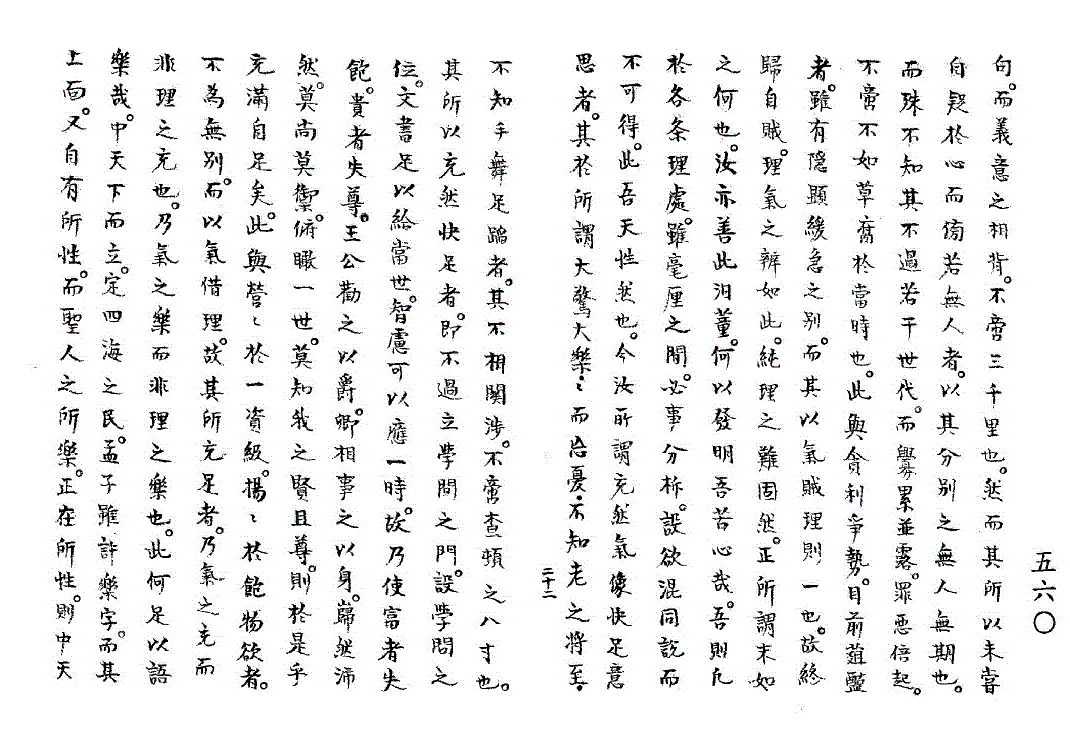 句。而义意之相背。不啻三千里也。然而其所以未尝自疑于心而傍若无人者。以其分别之无人无期也。而殊不知其不过若干世代。而衅累并露。罪恶倍起。不啻不如草腐于当时也。此与贪利争势。目前菹醢者。虽有隐显缓急之别。而其以气贼理则一也。故终归自贼。理气之辨如此。纯理之难固然。正所谓末如之何也。汝亦善此汩蕫。何以发明吾苦心哉。吾则凡于各条理处。虽毫厘之间。必事分析。设欲混同说而不可得。此吾天性然也。今汝所谓充然气像快足意思者。其于所谓大惊大乐,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手舞足蹈者。其不相关涉。不啻查顿之八寸也。其所以充然快足者。即不过立学问之门。设学问之位。文书足以给当世。智虑可以应一时。故乃使富者失饱。贵者失尊。王公劝之以爵。卿相事之以身。岿然沛然。莫尚莫御。俯瞰一世。莫知我之贤且尊。则于是乎充满自足矣。此与营营于一资级。扬扬于饱物欲者。不为无别。而以气借理。故其所充足者。乃气之充而非理之充也。乃气之乐而非理之乐也。此何足以语乐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孟子虽许乐字。而其上面。又自有所性。而圣人之所乐。正在所性。则中天
句。而义意之相背。不啻三千里也。然而其所以未尝自疑于心而傍若无人者。以其分别之无人无期也。而殊不知其不过若干世代。而衅累并露。罪恶倍起。不啻不如草腐于当时也。此与贪利争势。目前菹醢者。虽有隐显缓急之别。而其以气贼理则一也。故终归自贼。理气之辨如此。纯理之难固然。正所谓末如之何也。汝亦善此汩蕫。何以发明吾苦心哉。吾则凡于各条理处。虽毫厘之间。必事分析。设欲混同说而不可得。此吾天性然也。今汝所谓充然气像快足意思者。其于所谓大惊大乐,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手舞足蹈者。其不相关涉。不啻查顿之八寸也。其所以充然快足者。即不过立学问之门。设学问之位。文书足以给当世。智虑可以应一时。故乃使富者失饱。贵者失尊。王公劝之以爵。卿相事之以身。岿然沛然。莫尚莫御。俯瞰一世。莫知我之贤且尊。则于是乎充满自足矣。此与营营于一资级。扬扬于饱物欲者。不为无别。而以气借理。故其所充足者。乃气之充而非理之充也。乃气之乐而非理之乐也。此何足以语乐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孟子虽许乐字。而其上面。又自有所性。而圣人之所乐。正在所性。则中天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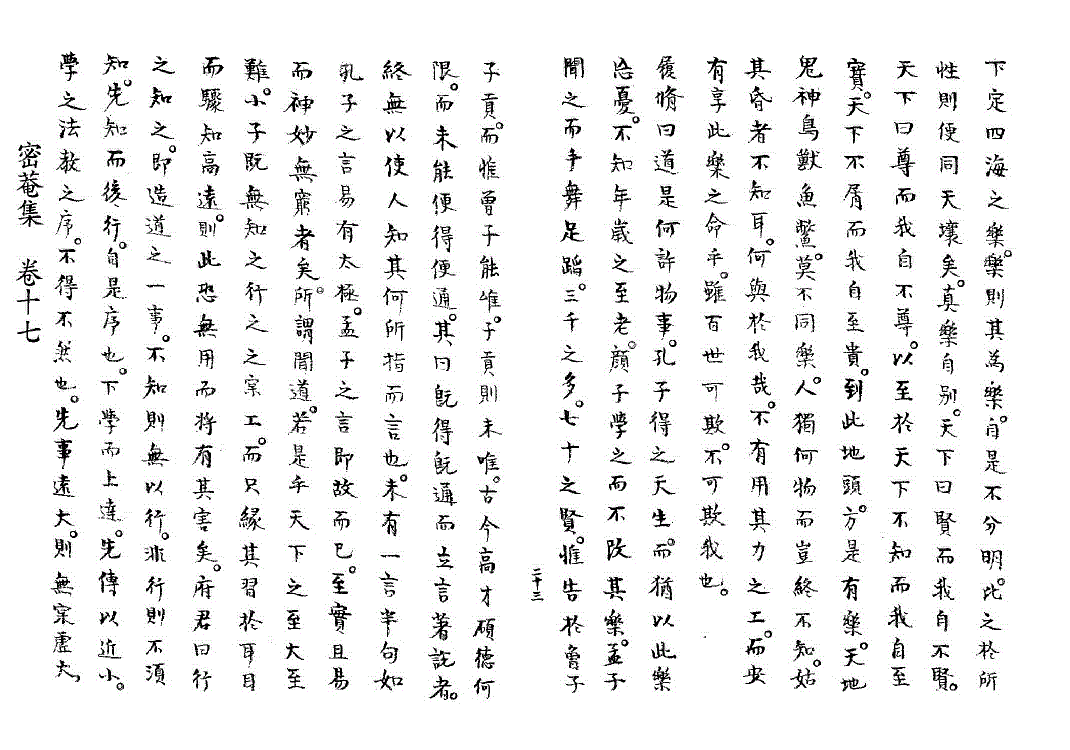 下定四海之乐。乐则其为乐。自是不分明。比之于所性则便同天壤矣。真乐自别。天下曰贤而我自不贤。天下曰尊而我自不尊。以至于天下不知而我自至宝。天下不屑而我自至贵。到此地头。方是有乐。天地鬼神鸟兽鱼鳖。莫不同乐。人独何物而岂终不知。姑其昏者不知耳。何与于我哉。不有用其力之工。而安有享此乐之命乎。虽百世可欺。不可欺我也。
下定四海之乐。乐则其为乐。自是不分明。比之于所性则便同天壤矣。真乐自别。天下曰贤而我自不贤。天下曰尊而我自不尊。以至于天下不知而我自至宝。天下不屑而我自至贵。到此地头。方是有乐。天地鬼神鸟兽鱼鳖。莫不同乐。人独何物而岂终不知。姑其昏者不知耳。何与于我哉。不有用其力之工。而安有享此乐之命乎。虽百世可欺。不可欺我也。履脩曰道是何许物事。孔子得之天生。而犹以此乐忘忧。不知年岁之至老。颜子学之而不改其乐。孟子闻之而手舞足蹈。三千之多。七十之贤。惟告于曾子子贡。而惟曾子能唯。子贡则未唯。古今高才硕德何限。而未能便得便通。其曰既得既通而立言著说者。终无以使人知其何所指而言也。未有一言半句如孔子之言易有太极。孟子之言即故而已。至实且易而神妙无穷者矣。所谓闻道。若是乎天下之至大至难。小子既无知之行之之宲工。而只缘其习于耳目而骤知高远。则此恐无用而将有其害矣。府君曰行之知之。即造道之一事。不知则无以行。非行则不须知。先知而后行。自是序也。下学而上达。先传以近小。学之法教之序。不得不然也。先事远大。则无宲虚大。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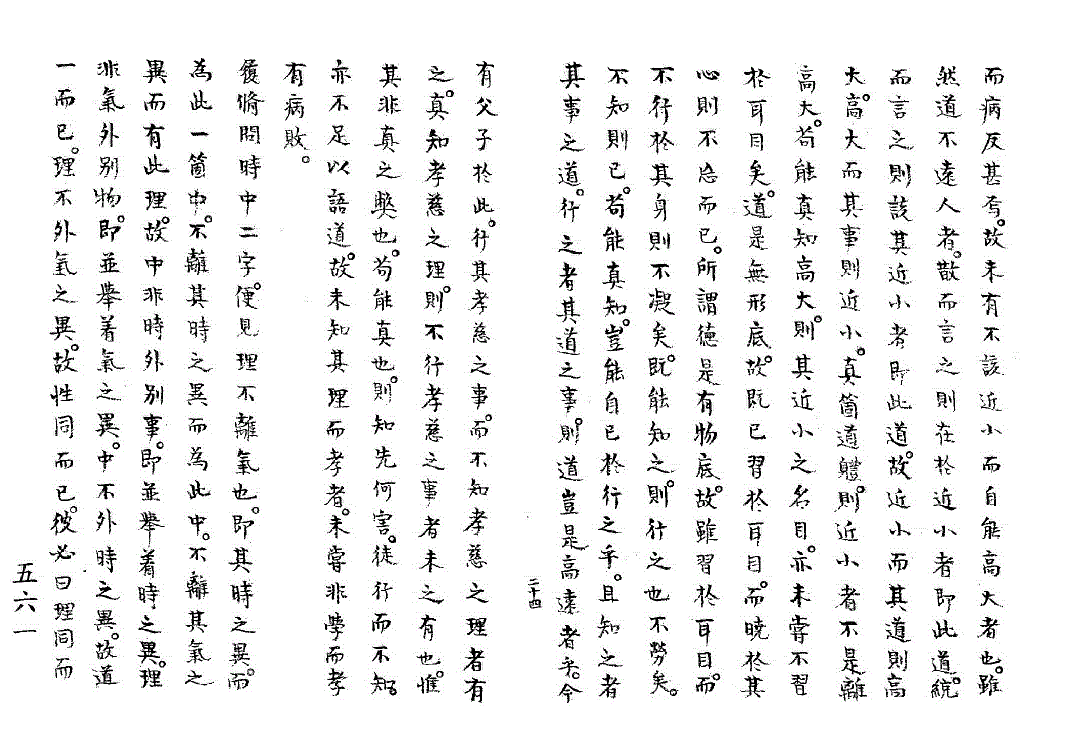 而病反甚焉。故未有不该近小而自能高大者也。虽然道不远人者。散而言之则在于近小者即此道。统而言之则该其近小者即此道。故近小而其道则高大。高大而其事则近小。真个道体。则近小者不是离高大。苟能真知高大。则其近小之名目。亦未尝不习于耳目矣。道是无形底。故既已习于耳目。而晓于其心则不忘而已。所谓德是有物底。故虽习于耳目。而不行于其身则不凝矣。既能知之。则行之也不劳矣。不知则已。苟能真知。岂能自已于行之乎。且知之者其事之道。行之者其道之事。则道岂是高远者乎。今有父子于此。行其孝慈之事。而不知孝慈之理者有之。真知孝慈之理。则不行孝慈之事者未之有也。惟其非真之弊也。苟能真也。则知先何害。徒行而不知。亦不足以语道。故未知其理而孝者。未尝非学而孝有病败。
而病反甚焉。故未有不该近小而自能高大者也。虽然道不远人者。散而言之则在于近小者即此道。统而言之则该其近小者即此道。故近小而其道则高大。高大而其事则近小。真个道体。则近小者不是离高大。苟能真知高大。则其近小之名目。亦未尝不习于耳目矣。道是无形底。故既已习于耳目。而晓于其心则不忘而已。所谓德是有物底。故虽习于耳目。而不行于其身则不凝矣。既能知之。则行之也不劳矣。不知则已。苟能真知。岂能自已于行之乎。且知之者其事之道。行之者其道之事。则道岂是高远者乎。今有父子于此。行其孝慈之事。而不知孝慈之理者有之。真知孝慈之理。则不行孝慈之事者未之有也。惟其非真之弊也。苟能真也。则知先何害。徒行而不知。亦不足以语道。故未知其理而孝者。未尝非学而孝有病败。履脩问时中二字。便见理不离气也。即其时之异。而为此一个中。不离其时之异而为此中。不离其气之异而有此理。故中非时外别事。即并举着时之异。理非气外别物。即并举着气之异。中不外时之异。故道一而已。理不外气之异。故性同而已。彼必曰理同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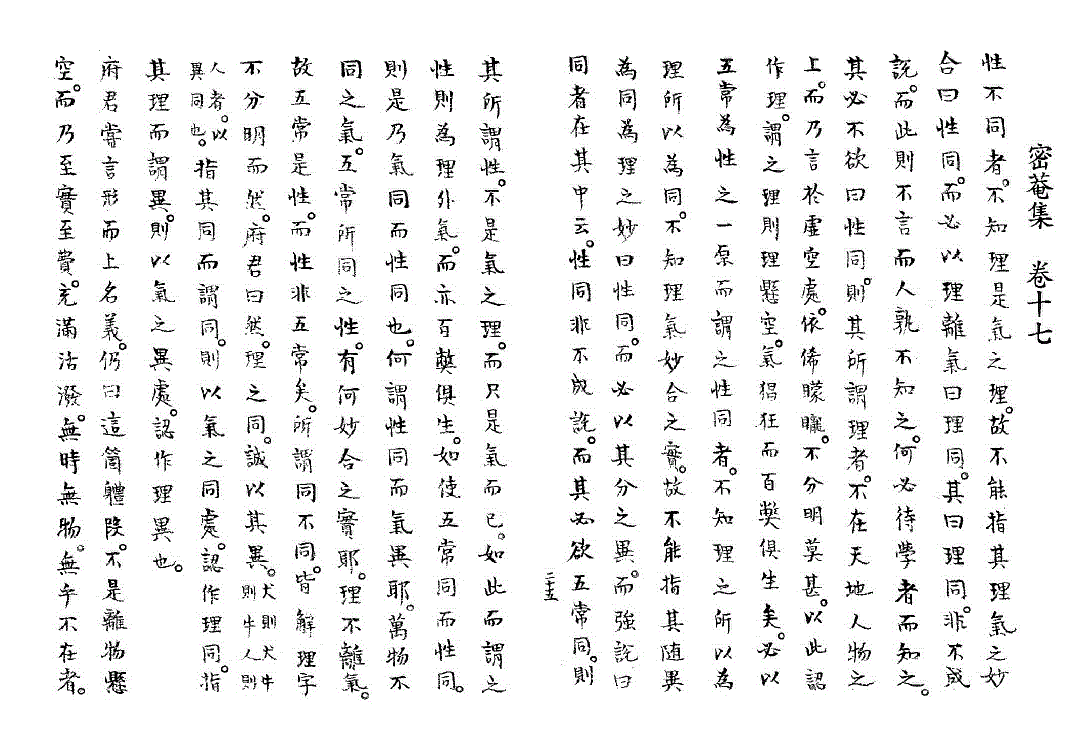 性不同者。不知理是气之理。故不能指其理气之妙合曰性同。而必以理离气曰理同。其曰理同。非不成说。而此则不言而人孰不知之。何必待学者而知之。其必不欲曰性同。则其所谓理者。不在天地人物之上。而乃言于虚空处。依俙矇眬。不分明莫甚。以此认作理。谓之理则理悬空。气猖狂而百弊俱生矣。必以五常为性之一原而谓之性同者。不知理之所以为理所以为同。不知理气妙合之实。故不能指其随异为同为理之妙曰性同。而必以其分之异。而强说曰同者在其中云。性同非不成说。而其必欲五常同。则其所谓性。不是气之理。而只是气而已。如此而谓之性则为理外气。而亦百弊俱生。如使五常同而性同。则是乃气同而性同也。何谓性同而气异耶。万物不同之气。五常所同之性。有何妙合之实耶。理不离气。故五常是性。而性非五常矣。所谓同不同。皆解理字不分明而然。府君曰然。理之同。诚以其异。(犬则犬牛则牛人则人者。以异同也。)指其同而谓同。则以气之同处。认作理同。指其理而谓异。则以气之异处。认作理异也。
性不同者。不知理是气之理。故不能指其理气之妙合曰性同。而必以理离气曰理同。其曰理同。非不成说。而此则不言而人孰不知之。何必待学者而知之。其必不欲曰性同。则其所谓理者。不在天地人物之上。而乃言于虚空处。依俙矇眬。不分明莫甚。以此认作理。谓之理则理悬空。气猖狂而百弊俱生矣。必以五常为性之一原而谓之性同者。不知理之所以为理所以为同。不知理气妙合之实。故不能指其随异为同为理之妙曰性同。而必以其分之异。而强说曰同者在其中云。性同非不成说。而其必欲五常同。则其所谓性。不是气之理。而只是气而已。如此而谓之性则为理外气。而亦百弊俱生。如使五常同而性同。则是乃气同而性同也。何谓性同而气异耶。万物不同之气。五常所同之性。有何妙合之实耶。理不离气。故五常是性。而性非五常矣。所谓同不同。皆解理字不分明而然。府君曰然。理之同。诚以其异。(犬则犬牛则牛人则人者。以异同也。)指其同而谓同。则以气之同处。认作理同。指其理而谓异。则以气之异处。认作理异也。府君尝言形而上名义。仍曰这个体段。不是离物悬空。而乃至实至费。充满活泼。无时无物。无乎不在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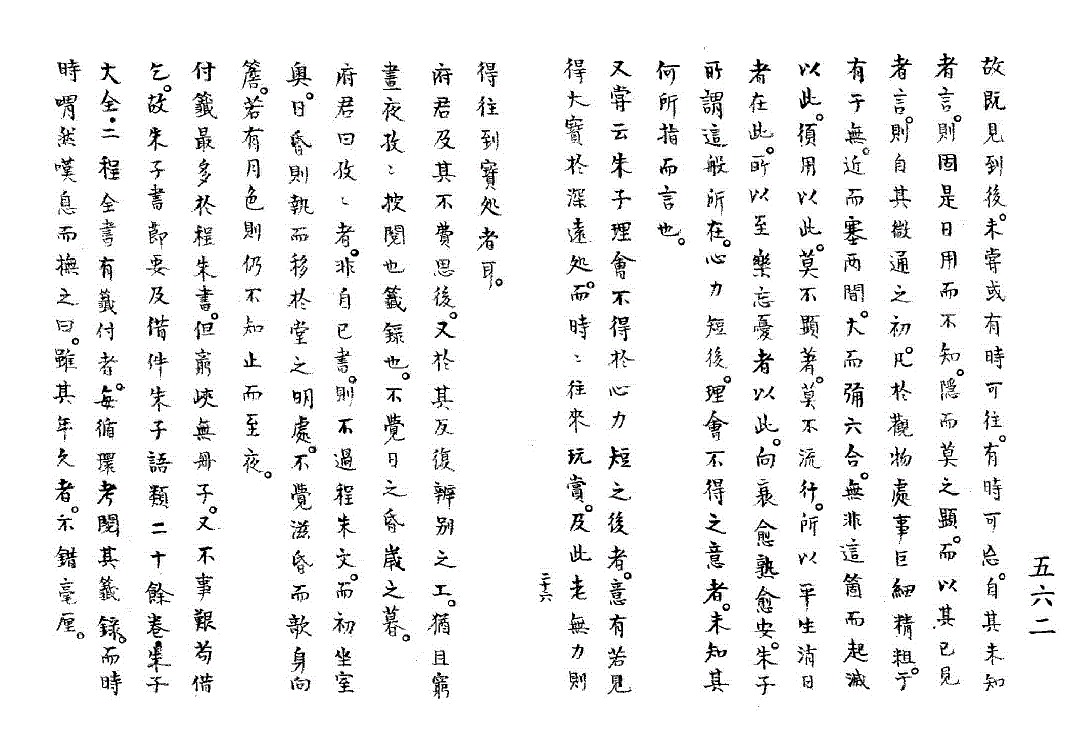 故既见到后。未尝或有时可往。有时可忘。自其未知者言。则固是日用而不知。隐而莫之显。而以其已见者言。则自其微通之初。凡于观物处事巨细精粗。于有于无。近而塞两间。大而弥六合。无非这个而起灭以此。须用以此。莫不显著。莫不流行。所以平生消日者在此。所以至乐忘忧者以此。向衰愈熟愈安。朱子所谓这般所在。心力短后。理会不得之意者。未知其何所指而言也。
故既见到后。未尝或有时可往。有时可忘。自其未知者言。则固是日用而不知。隐而莫之显。而以其已见者言。则自其微通之初。凡于观物处事巨细精粗。于有于无。近而塞两间。大而弥六合。无非这个而起灭以此。须用以此。莫不显著。莫不流行。所以平生消日者在此。所以至乐忘忧者以此。向衰愈熟愈安。朱子所谓这般所在。心力短后。理会不得之意者。未知其何所指而言也。又尝云朱子理会不得于心力短之后者。意有若见得大宝于深远处。而时时往来玩赏。及此老无力则得往到宝处者耳。
府君及其不费思后。又于其反复辨别之工。独且穷昼夜孜孜披阅也签录也。不觉日之昏岁之暮。
府君曰孜孜者。非自己书。则不过程朱文。而初坐室奥。日昏则执而移于堂之明处。不觉滋昏而欹身向檐。若有月色则仍不知止而至夜。
付签最多于程朱书。但穷峡无册子。又不事艰苟借乞。故朱子书节要及借件朱子语类二十馀卷,朱子大全,二程全书有签付者。每循环考阅其签录。而时时喟然叹息而抚之曰。虽其年久者。不错毫厘。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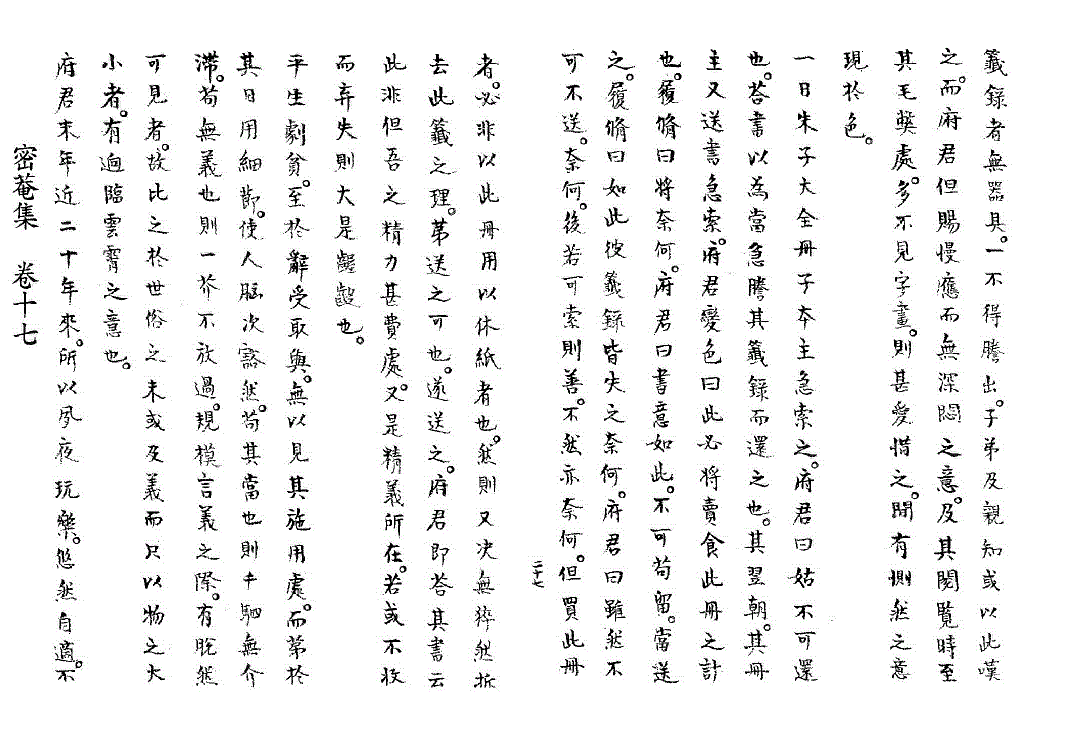 签录者无器具。一不得誊出。子弟及亲知或以此叹之。而府君但赐慢应而无深闷之意。及其阅览时至其毛弊处。多不见字画。则甚爱惜之。间有恻然之意现于色。
签录者无器具。一不得誊出。子弟及亲知或以此叹之。而府君但赐慢应而无深闷之意。及其阅览时至其毛弊处。多不见字画。则甚爱惜之。间有恻然之意现于色。一日朱子大全册子本主急索之。府君曰姑不可还也。答书以为当急誊其签录而还之也。其翌朝。其册主又送书急索。府君变色曰此必将卖食此册之计也。履脩曰将奈何。府君曰书意如此。不可苟留。当送之。履脩曰如此彼签录皆失之奈何。府君曰虽然不可不送。奈何。后若可索则善。不然亦奈何。但买此册者。必非以此册用以休纸者也。然则又决无猝然折去此签之理。第送之可也。遂送之。府君即答其书云此非但吾之精力甚费处。又是精义所在。若或不收而弃失则大是龌龊也。
平生剧贫。至于辞受取与。无以见其施用处。而第于其日用细节。使人胸次豁然。苟其当也则千驷无介滞。苟无义也则一芥不放过。规模言义之际。有脱然可见者。故比之于世俗之末或及义而只以物之大小者。有迥临云霄之意也。
府君末年近二十年来。所以夙夜玩乐。悠然自适。不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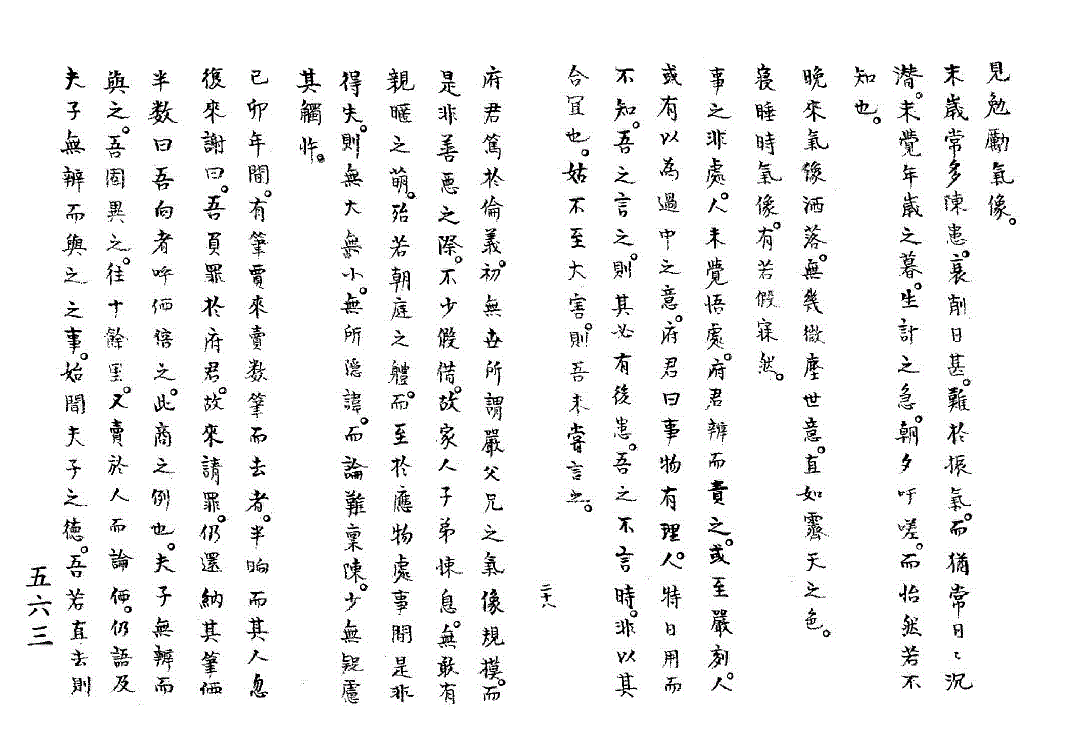 见勉励气像。
见勉励气像。末岁常多陈患。衰削日甚。难于振气。而犹常日日沉潜。未觉年岁之暮。生计之急。朝夕吁嗟。而怡然若不知也。
晚来气像洒落。无几微尘世意。直如霁天之色。
寝睡时气像。有若假寐然。
事之非处。人未觉吾处。府君辨而责之。或至严刻。人或有以为过中之意。府君曰事物有理。人特日用而不知。吾之言之。则其必有后患。吾之不言时。非以其合宜也。姑不至大害。则吾未尝言之。
府君笃于伦义。初无世所谓严父兄之气像规模。而是非善恶之际。不少假借。故家人子弟悚息。无敢有亲昵之萌。殆若朝庭之体。而至于应物处事间是非得失。则无大无小。无所隐讳。而论难禀陈。少无疑虑其触忤。
己卯年间。有笔贾来卖数笔而去者。半晌而其人忽复来谢曰。吾负罪于府君。故来请罪。仍还纳其笔价半数曰吾向者呼价倍之。此商之例也。夫子无辨而与之。吾固异之。往十馀里。又卖于人而论价。仍语及夫子无辨而与之之事。始闻夫子之德。吾若直去则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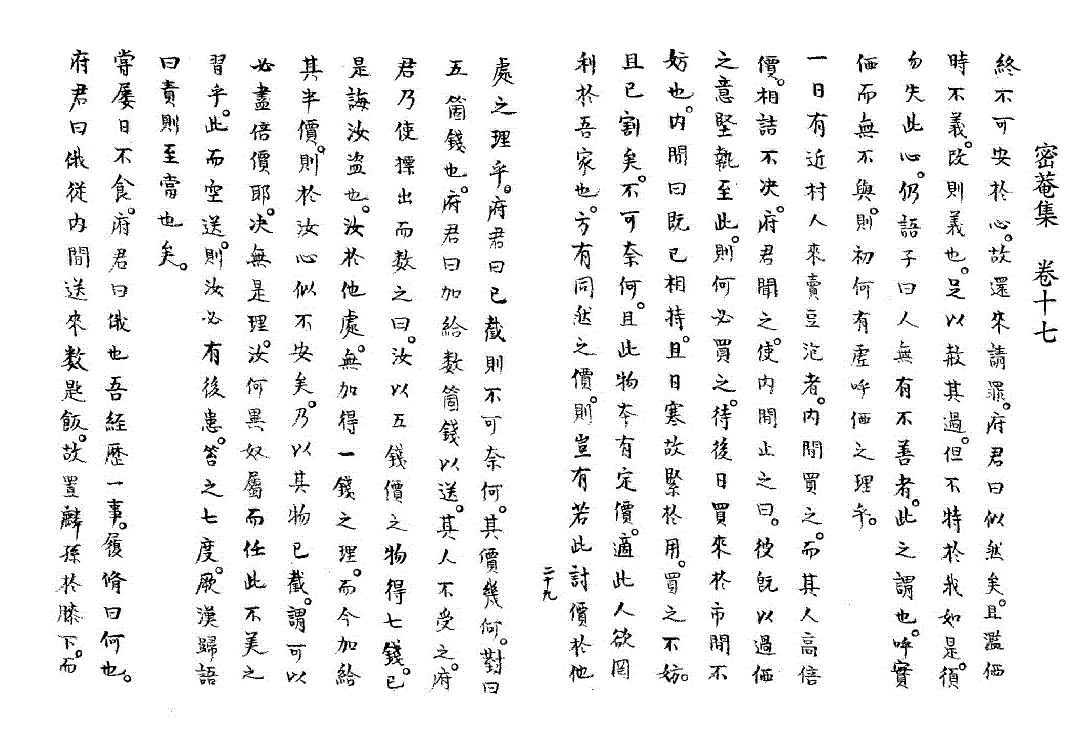 终不可安于心。故还来请罪。府君曰似然矣。且滥价时不义。改则义也。足以赦其过。但不特于我如是。须勿失此心。仍语子曰人无有不善者。此之谓也。呼实价而无不与。则初何有虚呼价之理乎。
终不可安于心。故还来请罪。府君曰似然矣。且滥价时不义。改则义也。足以赦其过。但不特于我如是。须勿失此心。仍语子曰人无有不善者。此之谓也。呼实价而无不与。则初何有虚呼价之理乎。一日有近村人来卖豆泡者。内间买之。而其人高倍价。相诘不决。府君闻之。使内间止之曰。彼既以过价之意坚执至此。则何必买之。待后日买来于市间不妨也。内间曰既已相持。且日寒故紧于用。买之不妨。且已割矣。不可奈何。且此物本有定价。适此人欲罔利于吾家也。方有同然之价。则岂有若此讨价于他处之理乎。府君曰已截则不可奈何。其价几何。对曰五个钱也。府君曰加给数个钱以送。其人不受之。府君乃使摽出而数之曰。汝以五钱价之物得七钱。已是诲汝盗也。汝于他处。无加得一钱之理。而今加给其半价。则于汝心似不安矣。乃以其物已截。谓可以必尽倍价耶。决无是理。汝何异奴属而任此不美之习乎。此而空送。则汝必有后患。笞之七度。厥汉归语曰责则至当也矣。
尝屡日不食。府君曰俄也吾经历一事。履脩曰何也。府君曰俄从内间送来数匙饭。故置麟孙于膝下。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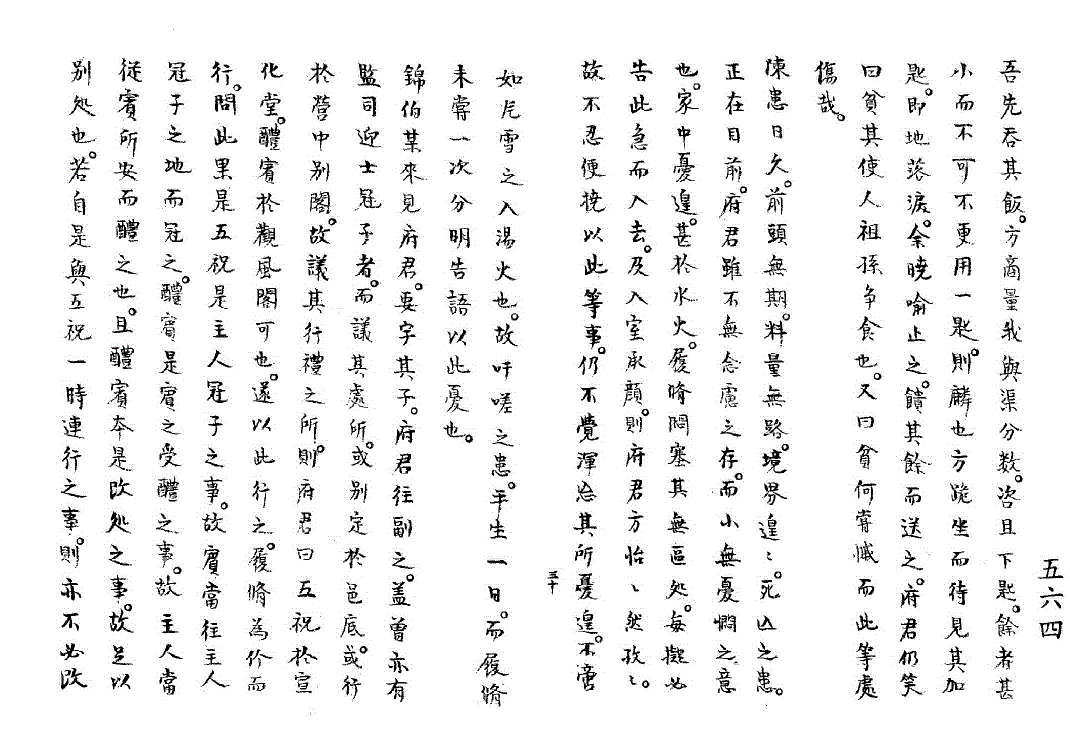 吾先吞其饭。方商量我与渠分数。咨且下匙。馀者甚小而不可不更用一匙。则麟也方跪坐而待见其加匙。即地落泪。余晓喻止之。馈其馀而送之。府君仍笑曰贫其使人祖孙争食也。又曰贫何尝戚而此等处伤哉。
吾先吞其饭。方商量我与渠分数。咨且下匙。馀者甚小而不可不更用一匙。则麟也方跪坐而待见其加匙。即地落泪。余晓喻止之。馈其馀而送之。府君仍笑曰贫其使人祖孙争食也。又曰贫何尝戚而此等处伤哉。陈患日久。前头无期。料量无路。境界遑遑。死亡之患。正在目前。府君虽不无念虑之存。而小无忧懑之意也。家中忧遑。甚于水火。履脩闷塞其无区处。每拟必告此急而入去。及入室承颜。则府君方怡怡然孜孜。故不忍便挠以此等事。仍不觉浑忘其所忧遑。不啻如片雪之入汤火也。故吁嗟之患。平生一日。而履脩未尝一次分明告语以此忧也。
锦伯某来见府君。要字其子。府君往副之。盖曾亦有监司迎士冠子者。而议其处所。或别定于邑底。或行于营中别阁。故议其行礼之所。则府君曰五祝于宣化堂。醴宾于观风阁可也。遂以此行之。履脩为价而行。问此果是五祝是主人冠子之事。故宾当往主人冠子之地而冠之。醴宾是宾之受醴之事。故主人当从宾所安而醴之也。且醴宾本是改处之事。故足以别处也。若自是与五祝一时连行之事。则亦不必改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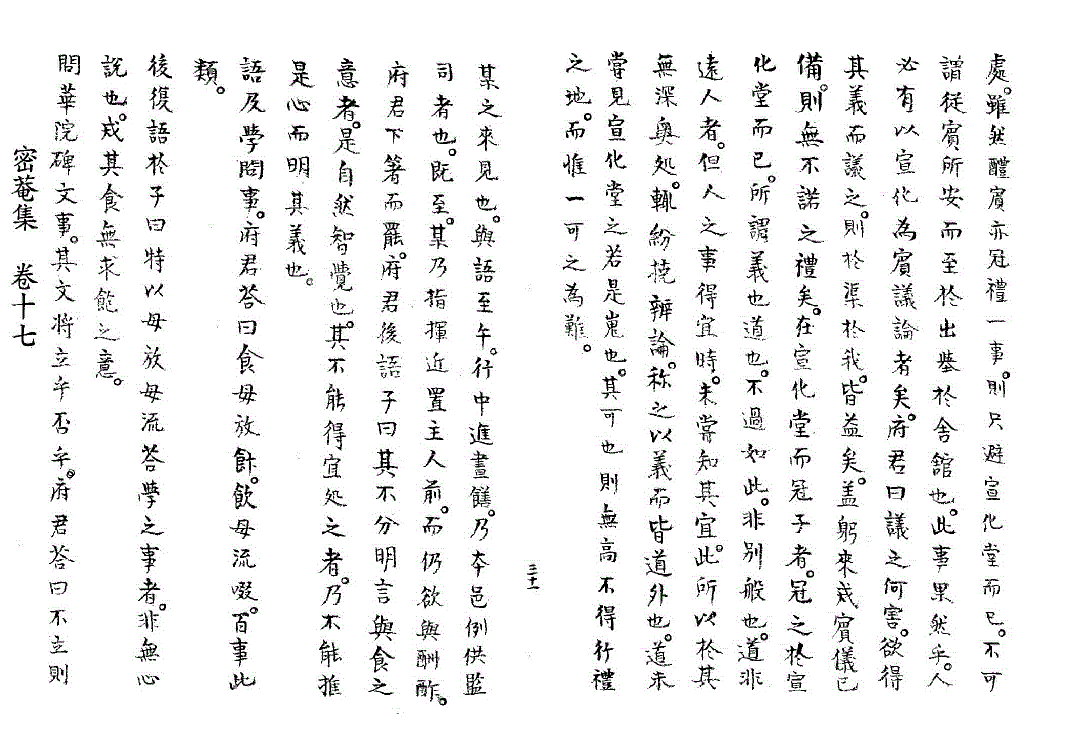 处。虽然醴宾亦冠礼一事。则只避宣化堂而已。不可谓从宾所安而至于出举于舍馆也。此事果然乎。人必有以宣化为宾议论者矣。府君曰议之何害。欲得其义而议之。则于渠于我。皆益矣。盖躬来戒宾仪已备。则无不诺之礼矣。在宣化堂而冠子者。冠之于宣化堂而已。所谓义也道也。不过如此。非别般也。道非远人者。但人之事得宜时。未尝知其宜。此所以于其无深奥处。辄纷挠辨论。称之以义而皆道外也。道未尝见宣化堂之若是嵬也。其可也则无高不得行礼之地。而惟一可之为难。
处。虽然醴宾亦冠礼一事。则只避宣化堂而已。不可谓从宾所安而至于出举于舍馆也。此事果然乎。人必有以宣化为宾议论者矣。府君曰议之何害。欲得其义而议之。则于渠于我。皆益矣。盖躬来戒宾仪已备。则无不诺之礼矣。在宣化堂而冠子者。冠之于宣化堂而已。所谓义也道也。不过如此。非别般也。道非远人者。但人之事得宜时。未尝知其宜。此所以于其无深奥处。辄纷挠辨论。称之以义而皆道外也。道未尝见宣化堂之若是嵬也。其可也则无高不得行礼之地。而惟一可之为难。某之来见也。与语至午。行中进昼膳。乃本邑例供监司者也。既至。某乃指挥近置主人前。而仍欲与酬酢。府君下箸而罢。府君后语子曰其不分明言与食之意者。是自然智觉也。其不能得宜处之者。乃不能推是心而明其义也。
语及学问事。府君答曰食毋放饭。饮毋流啜。百事此类。
后复语于子曰特以毋放毋流答学之事者。非无心说也。戒其食无求饱之意。
问华院碑文事。其文将立乎否乎。府君答曰不立则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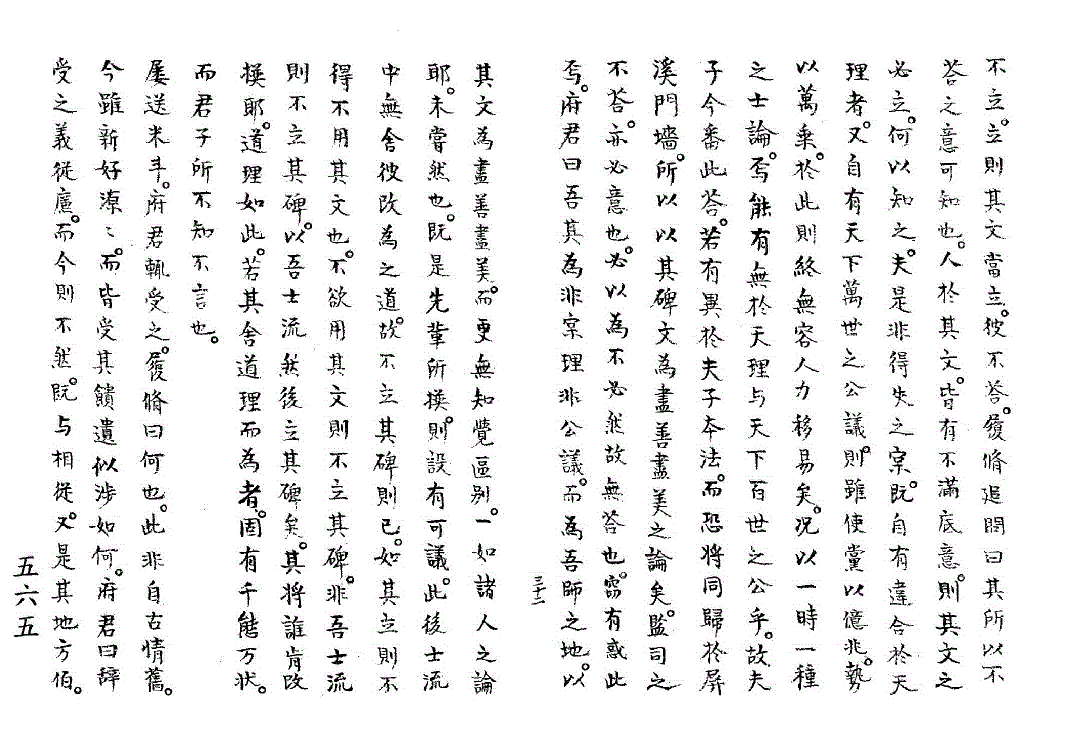 不立。立则其文当立。彼不答。履脩追问曰其所以不答之意可知也。人于其文。皆有不满底意。则其文之必立。何以知之。夫是非得失之宲。既自有违合于天理者。又自有天下万世之公议。则虽使党以亿兆。势以万乘。于此则终无容人力移易矣。况以一时一种之士论。焉能有无于天理与天下百世之公乎。故夫子今番此答。若有异于夫子本法。而恐将同归于屏溪门墙。所以以其碑文为尽善尽美之论矣。监司之不答。亦必意也。必以为不必然故无答也。窃有惑此焉。府君曰吾其为非宲理非公议。而为吾师之地。以其文为尽善尽美。而更无知觉区别。一如诸人之论耶。未尝然也。既是先辈所撰。则设有可议。此后士流中无舍彼改为之道。故不立其碑则已。如其立则不得不用其文也。不欲用其文则不立其碑。非吾士流则不立其碑。以吾士流然后立其碑矣。其将谁肯改撰耶。道理如此。若其舍道理而为者。固有千态万状。而君子所不知不言也。
不立。立则其文当立。彼不答。履脩追问曰其所以不答之意可知也。人于其文。皆有不满底意。则其文之必立。何以知之。夫是非得失之宲。既自有违合于天理者。又自有天下万世之公议。则虽使党以亿兆。势以万乘。于此则终无容人力移易矣。况以一时一种之士论。焉能有无于天理与天下百世之公乎。故夫子今番此答。若有异于夫子本法。而恐将同归于屏溪门墙。所以以其碑文为尽善尽美之论矣。监司之不答。亦必意也。必以为不必然故无答也。窃有惑此焉。府君曰吾其为非宲理非公议。而为吾师之地。以其文为尽善尽美。而更无知觉区别。一如诸人之论耶。未尝然也。既是先辈所撰。则设有可议。此后士流中无舍彼改为之道。故不立其碑则已。如其立则不得不用其文也。不欲用其文则不立其碑。非吾士流则不立其碑。以吾士流然后立其碑矣。其将谁肯改撰耶。道理如此。若其舍道理而为者。固有千态万状。而君子所不知不言也。屡送米斗。府君辄受之。履脩曰何也。此非自古情旧。今虽新好源源。而皆受其馈遗似涉如何。府君曰辞受之义从廉。而今则不然。既与相从。又是其地方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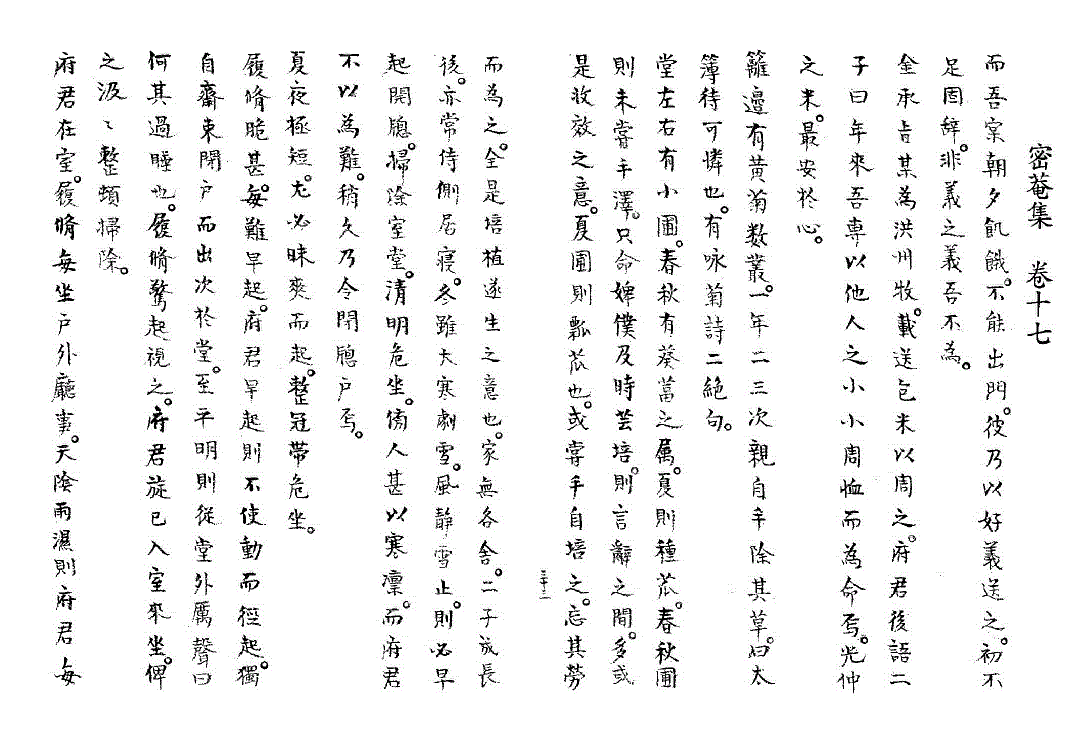 而吾宲朝夕饥饿。不能出门。彼乃以好义送之。初不足固辞。非义之义吾不为。
而吾宲朝夕饥饿。不能出门。彼乃以好义送之。初不足固辞。非义之义吾不为。金承旨某为洪州牧。载送包米以周之。府君后语二子曰年来吾专以他人之小小周恤而为命焉。光仲之米。最安于心。
篱边有黄菊数丛。一年二三次亲自手除其草。曰太薄待可怜也。有咏菊诗二绝句。
堂左右有小圃。春秋有葵葍之属。夏则种菰。春秋圃则未尝手泽。只命婢仆及时芸培。则言辞之间。多或是收效之意。夏圃则瓢菰也。或尝手自培之。忘其劳而为之。全是培植遂生之意也。家无各舍。二子成长后。亦常侍侧居寝。冬虽大寒剧雪。风静雪止。则必早起开窗。扫除室堂。清明危坐。傍人甚以寒凛。而府君不以为难。稍久乃令闭窗户焉。
夏夜极短。尤必昧爽而起。整冠带危坐。
履脩脆甚。每难早起。府君早起则不使动而径起。独自斋束闭户而出次于堂。至平明则从堂外厉声曰何其过睡也。履脩惊起视之。府君旋已入室来坐。俾之汲汲整顿扫除。
府君在室。履脩每坐户外厅事。天阴雨湿则府君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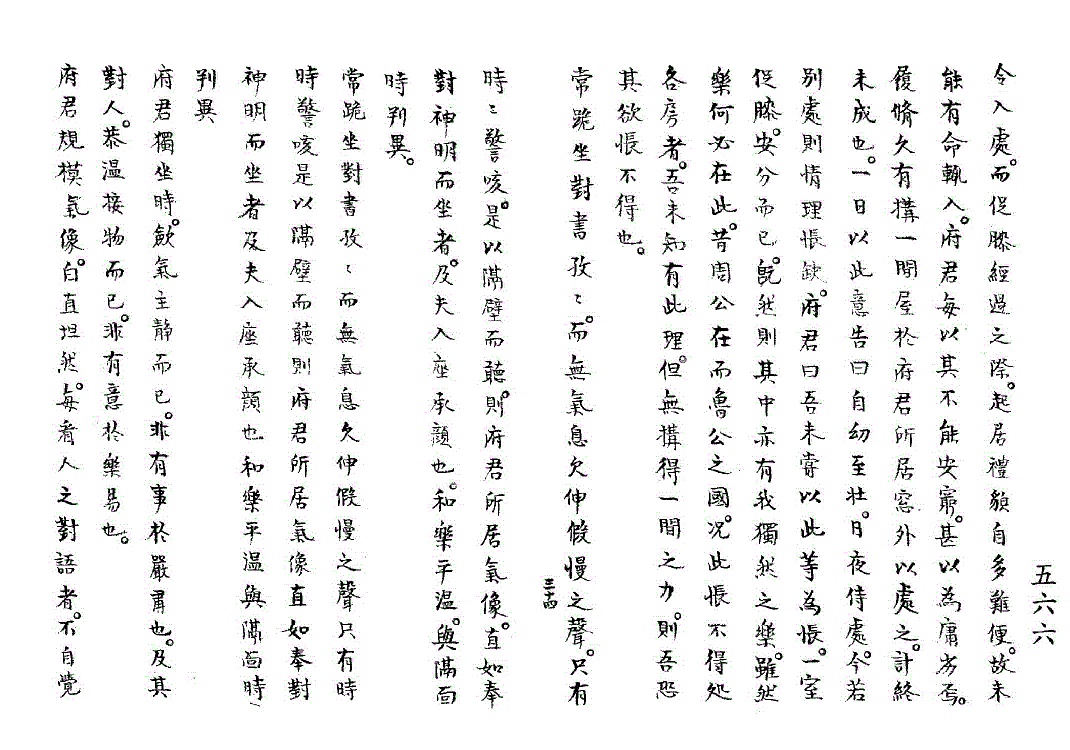 令入处。而促膝经过之际。起居礼貌自多难便。故未能有命辄入。府君每以其不能安穷。甚以为庸劣焉。
令入处。而促膝经过之际。起居礼貌自多难便。故未能有命辄入。府君每以其不能安穷。甚以为庸劣焉。履脩久有搆一间屋于府君所居窗外以处之。计终未成也。一日以此意告曰自幼至壮。日夜侍处。今若别处则情理怅缺。府君曰吾未尝以此等为怅。一室促膝。安分而已。既然则其中亦有我独然之乐。虽然乐何必在此。昔周公在而鲁公之国。况此怅不得处各房者。吾未知有此理。但无搆得一间之力。则吾恐其欲怅不得也。
常跪坐对书孜孜。而无气息欠伸假慢之声。只有时时警咳。是以隔壁而听。则府君所居气像。直如奉对神明而坐者。及夫入座承颜也。和乐平温。与隔面时判异。
常跪坐对书孜孜。而无气息欠伸假慢之声。只有时时警咳。是以隔壁而听。则府君所居气像。直如奉对神明。而坐者及夫入座承颜也。和乐平温。与隔面时判异。
府君独坐时。敛气主静而已。非有事于严肃也。及其对人。恭温接物而已。非有意于乐易也。
府君规模气像。白直坦然。每看人之对语者。不自觉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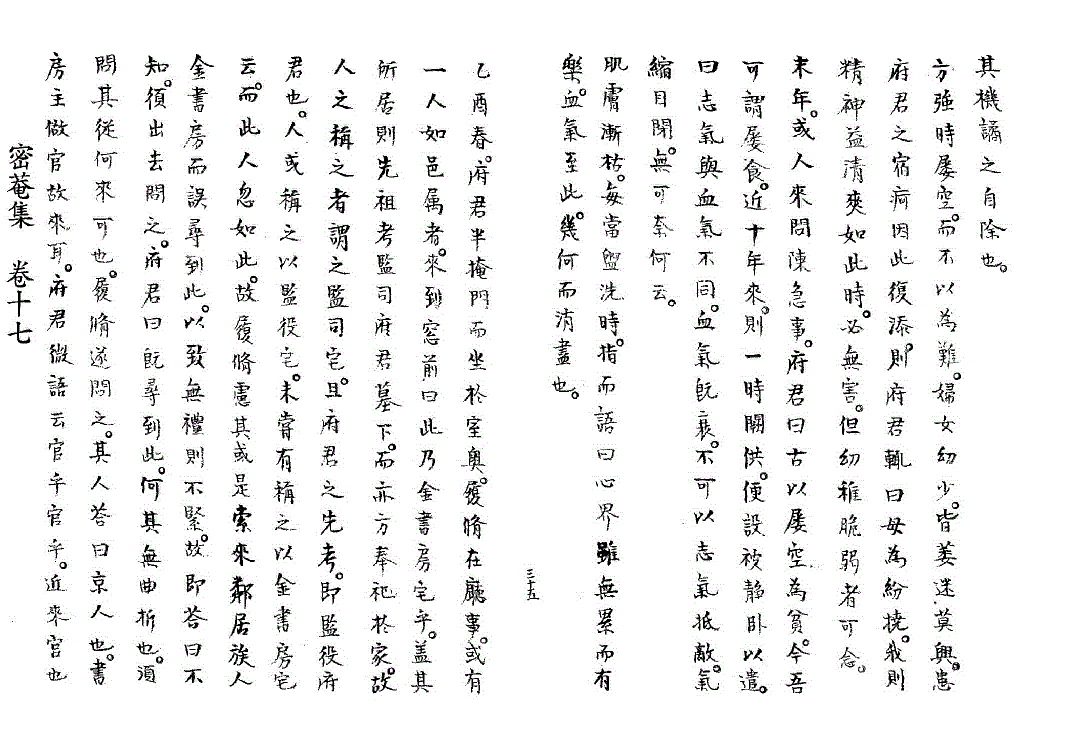 其机谲之自除也。
其机谲之自除也。方强时屡空。而不以为难。妇女幼少。皆萎迷莫兴。患府君之宿疴因此复添。则府君辄曰毋为纷挠。我则精神益清爽如此时。必无害。但幼稚脆弱者可念。
末年。或人来问陈急事。府君曰古以屡空为贫。今吾可谓屡食。近十年来。则一时阙供。便设被静卧以遣。曰志气与血气不同。血气既衰。不可以志气抵敌。气缩目闭。无可奈何云。
肌肤渐枯。每当盥洗时。指而语曰心界虽无累而有乐。血气至此。几何而消尽也。
乙酉春。府君半掩门而坐于室奥。履脩在厅事。或有一人如邑属者。来到窗前曰此乃金书房宅乎。盖其所居则先祖考监司府君墓下。而亦方奉祀于家。故人之称之者谓之监司宅。且府君之先考。即监役府君也。人或称之以监役宅。未尝有称之以金书房宅云。而此人忽如此。故履脩虑其或是索来邻居族人金书房而误寻到此。以致无礼则不紧。故即答曰不知。须出去问之。府君曰既寻到此。何其无曲折也。须问其从何来可也。履脩遂问之。其人答曰京人也。书房主做官故来耳。府君微语云官乎官乎。近来官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7L 页
 极难云。胡为乎来于我哉。太无理矣。仍即亲问之曰汝应以仓洞书(仓洞即从子履中兄弟所旅也。)来矣。纳之见书。则铨官乃金某沈某也。出送其人后。府君曰无论其于我用无用。而所谓官云者。太无苗脉也。再宿之。艰辛贷给归资百钱以送之。府君乃曰官果于我无益。而为穷山一场贷钱之劳矣。监隶之去也。告之曰案前行次何以为之。府君曰吾方病不能往。汝第还去。对曰然则有呈病所志。府君曰日限几何。曰三十日也。府君曰所志则当自京限前区处也。其后闻之。其人还京语人曰吾见异人也。往溪室新官宅时。数十里外闻之则皆知之。入其洞问之。村人指点越边白屋。故问书房主在家乎。答曰在矣。从何来乎。余曰京人也。村人曰其两班方在绝火。远人徒然将饿矣。余意以为必不免饿矣。且其贫穷如此。则得此官可喜。可知吾之入去。其生光当不少。入其扉则弊屋将颓。閒寂晏如。少无阙食遑悯之色。及其见面。乃朗然一书生。貌如童颜。非五十馀岁老人之饥饿者。而真仙人也。浑舍无闻官喜悦色。吾遂无聊空还。平生见异事于此云。府君闻而微笑曰其人久作缮工监隶。乃见怪底人也。
极难云。胡为乎来于我哉。太无理矣。仍即亲问之曰汝应以仓洞书(仓洞即从子履中兄弟所旅也。)来矣。纳之见书。则铨官乃金某沈某也。出送其人后。府君曰无论其于我用无用。而所谓官云者。太无苗脉也。再宿之。艰辛贷给归资百钱以送之。府君乃曰官果于我无益。而为穷山一场贷钱之劳矣。监隶之去也。告之曰案前行次何以为之。府君曰吾方病不能往。汝第还去。对曰然则有呈病所志。府君曰日限几何。曰三十日也。府君曰所志则当自京限前区处也。其后闻之。其人还京语人曰吾见异人也。往溪室新官宅时。数十里外闻之则皆知之。入其洞问之。村人指点越边白屋。故问书房主在家乎。答曰在矣。从何来乎。余曰京人也。村人曰其两班方在绝火。远人徒然将饿矣。余意以为必不免饿矣。且其贫穷如此。则得此官可喜。可知吾之入去。其生光当不少。入其扉则弊屋将颓。閒寂晏如。少无阙食遑悯之色。及其见面。乃朗然一书生。貌如童颜。非五十馀岁老人之饥饿者。而真仙人也。浑舍无闻官喜悦色。吾遂无聊空还。平生见异事于此云。府君闻而微笑曰其人久作缮工监隶。乃见怪底人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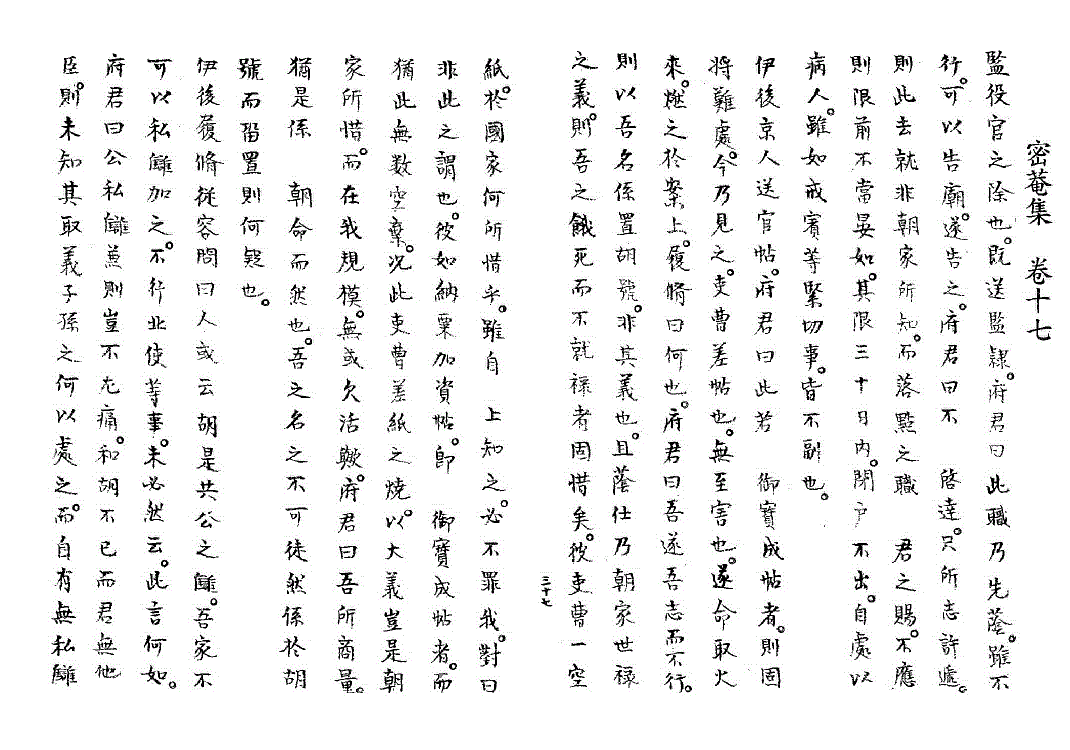 监役官之除也。既送监隶。府君曰此职乃先荫。虽不行。可以告庙。遂告之。府君曰不 启达。只所志许递。则此去就非朝家所知。而落点之职 君之赐。不应则限前不当晏如。其限三十日内。闭户不出。自处以病人。虽如戒宾等紧切事。皆不副也。
监役官之除也。既送监隶。府君曰此职乃先荫。虽不行。可以告庙。遂告之。府君曰不 启达。只所志许递。则此去就非朝家所知。而落点之职 君之赐。不应则限前不当晏如。其限三十日内。闭户不出。自处以病人。虽如戒宾等紧切事。皆不副也。伊后京人送官帖。府君曰此若 御宝成帖者。则固将难处。今乃见之。吏曹差帖也。无至害也。遂命取火来。燃之于案上。履脩曰何也。府君曰吾遂吾志而不行。则以吾名系置胡号。非其义也。且荫仕乃朝家世禄之义。则吾之饿死而不就禄者固惜矣。彼吏曹一空纸。于国家何所惜乎。虽自 上知之。必不罪我。对曰非此之谓也。彼如纳粟加资帖。即 御宝成帖者。而犹此无数空弃。况此吏曹差纸之烧。以大义岂是朝家所惜。而在我规模。无或欠活欤。府君曰吾所商量。犹是系 朝命而然也。吾之名之不可徒然系于胡号而留置则何疑也。
伊后履脩从容问曰人或云胡是共公之雠。吾家不可以私雠加之。不行北使等事。未必然云。此言何如。府君曰公私雠兼则岂不尤痛。和胡不已而君无他臣。则未知其取义子孙之何以处之。而自有无私雠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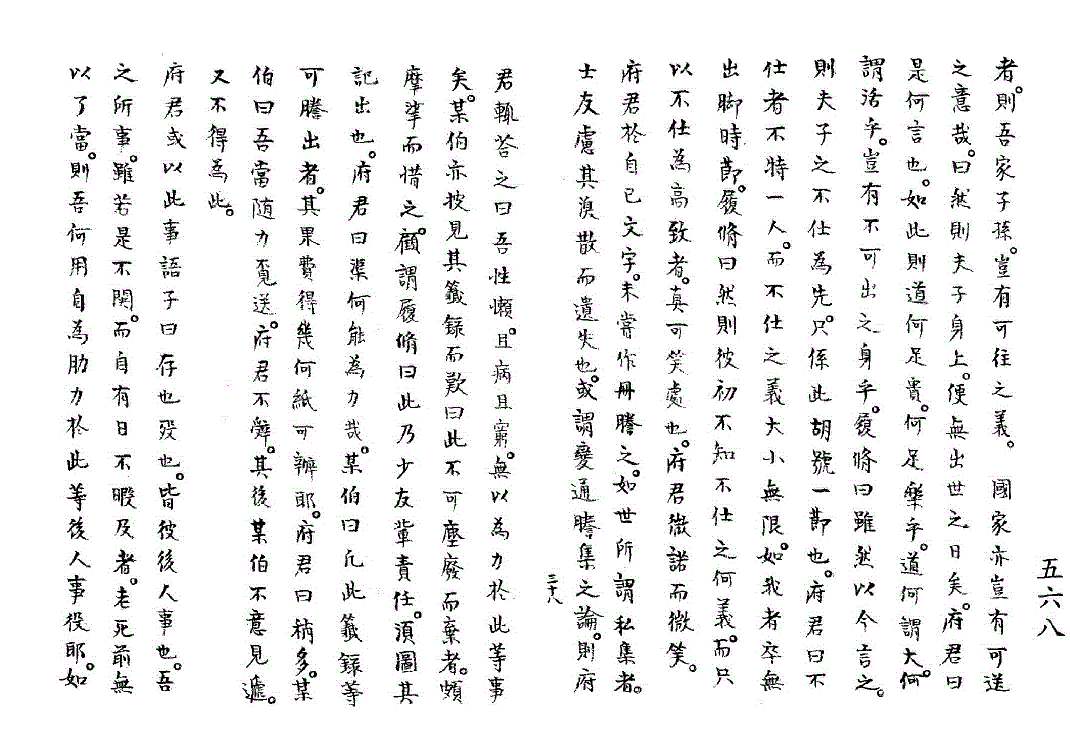 者。则吾家子孙。岂有可往之义。 国家亦岂有可送之意哉。曰然则夫子身上。便无出世之日矣。府君曰是何言也。如此则道何足贵。何足乐乎。道何谓大。何谓活乎。岂有不可出之身乎。履脩曰虽然以今言之。则夫子之不仕为先。只系此胡号一节也。府君曰不仕者不特一人。而不仕之义大小无限。如我者卒无出脚时节。履脩曰然则彼初不知不仕之何义。而只以不仕为高致者。真可笑处也。府君微诺而微笑。
者。则吾家子孙。岂有可往之义。 国家亦岂有可送之意哉。曰然则夫子身上。便无出世之日矣。府君曰是何言也。如此则道何足贵。何足乐乎。道何谓大。何谓活乎。岂有不可出之身乎。履脩曰虽然以今言之。则夫子之不仕为先。只系此胡号一节也。府君曰不仕者不特一人。而不仕之义大小无限。如我者卒无出脚时节。履脩曰然则彼初不知不仕之何义。而只以不仕为高致者。真可笑处也。府君微诺而微笑。府君于自己文字。未尝作册誊之。如世所谓私集者。士友虑其涣散而遗失也。或谓变通誊集之论。则府君辄答之曰吾性懒。且病且穷。无以为力于此等事矣。某伯亦披见其签录而叹曰此不可尘废而弃者。颇摩挲而惜之。顾谓履脩曰此乃少友辈责任。须图其记出也。府君曰渠何能为力哉。某伯曰凡此签录等可誊出者。其果费得几何纸可办耶。府君曰稍多。某伯曰吾当随力觅送。府君不辞。其后某伯不意见递。又不得为此。
府君或以此事语子曰存也殁也。皆彼后人事也。吾之所事。虽若是不关。而自有日不暇及者。老死前无以了当。则吾何用自为助力于此等后人事役耶。如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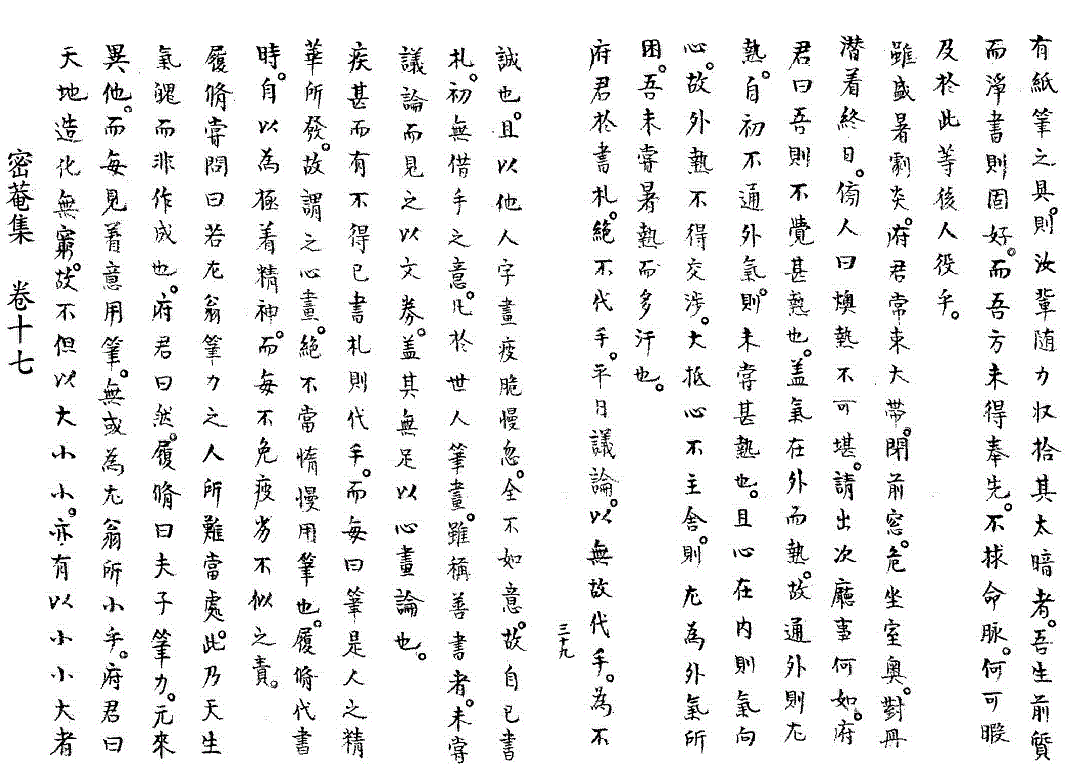 有纸笔之具。则汝辈随力收拾其太暗者。吾生前质而净书则固好。而吾方未得奉先。不救命脉。何可暇及于此等后人役乎。
有纸笔之具。则汝辈随力收拾其太暗者。吾生前质而净书则固好。而吾方未得奉先。不救命脉。何可暇及于此等后人役乎。虽盛暑剧炎。府君常束大带。闭前窗。危坐室奥。对册潜着终日。傍人曰燠热不可堪。请出次厅事何如。府君曰吾则不觉甚热也。盖气在外而热。故通外则尤热。自初不通外气。则未尝甚热也。且心在内则气向心。故外热不得交涉。大抵心不主舍。则尤为外气所困。吾未尝暑热而多汗也。
府君于书札。绝不代手。平日议论。以无故代手。为不诚也。且以他人字画疲脆慢忽。全不如意。故自己书札。初无借手之意。凡于世人笔画。虽称善书者。未尝议论而见之以文券。盖其无足以心画论也。
疾甚而有不得已书札则代手。而每曰笔是人之精华所发。故谓之心画。绝不当惰慢用笔也。履脩代书时。自以为极着精神。而每不免疲劣不似之责。
履脩尝问曰若尤翁笔力之人所难当处。此乃天生气魄而非作成也。府君曰然。履脩曰夫子笔力。元来异他。而每见着意用笔。无或为尤翁所小乎。府君曰天地造化无穷。故不但以大小小。亦有以小小大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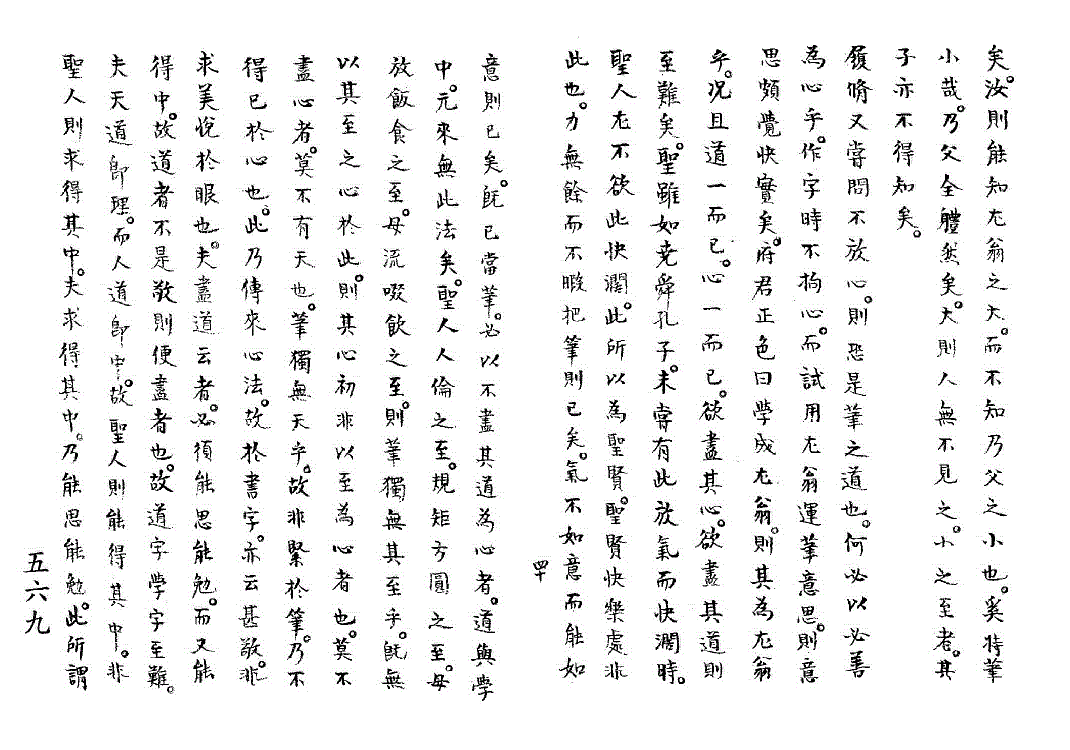 矣。汝则能知尤翁之大。而不知乃父之小也。奚持笔小哉。乃父全体然矣。大则人无不见之。小之至者。其子亦不得知矣。
矣。汝则能知尤翁之大。而不知乃父之小也。奚持笔小哉。乃父全体然矣。大则人无不见之。小之至者。其子亦不得知矣。履脩又尝问不放心。则恐是笔之道也。何必以必善为心乎。作字时不拘心。而试用尤翁运笔意思。则意思颇觉快实矣。府君正色曰学成尤翁。则其为尤翁乎。况且道一而已。心一而已。欲尽其心。欲尽其道则至难矣。圣虽如尧舜孔子。未尝有此放气而快阔时。圣人尤不欲此快阔。此所以为圣贤。圣贤快乐处非此也。力无馀而不暇把笔则已矣。气不如意而能如意则已矣。既已当笔。必以不尽其道为心者。道与学中。元来无此法矣。圣人人伦之至。规矩方圆之至。毋放饭食之至。毋流啜饮之至。则笔独无其至乎。既无以其至之心于此。则其心初非以至为心者也。莫不尽心者。莫不有天也。笔独无天乎。故非紧于笔。乃不得已于心也。此乃传来心法。故于书字。亦云甚敬。非求美悦于眼也。夫尽道云者。必须能思能勉。而又能得中。故道者不是敬则便尽者也。故道字学字至难。夫天道即理。而人道即中。故圣人则能得其中。非圣人则求得其中。夫求得其中。乃能思能勉。此所谓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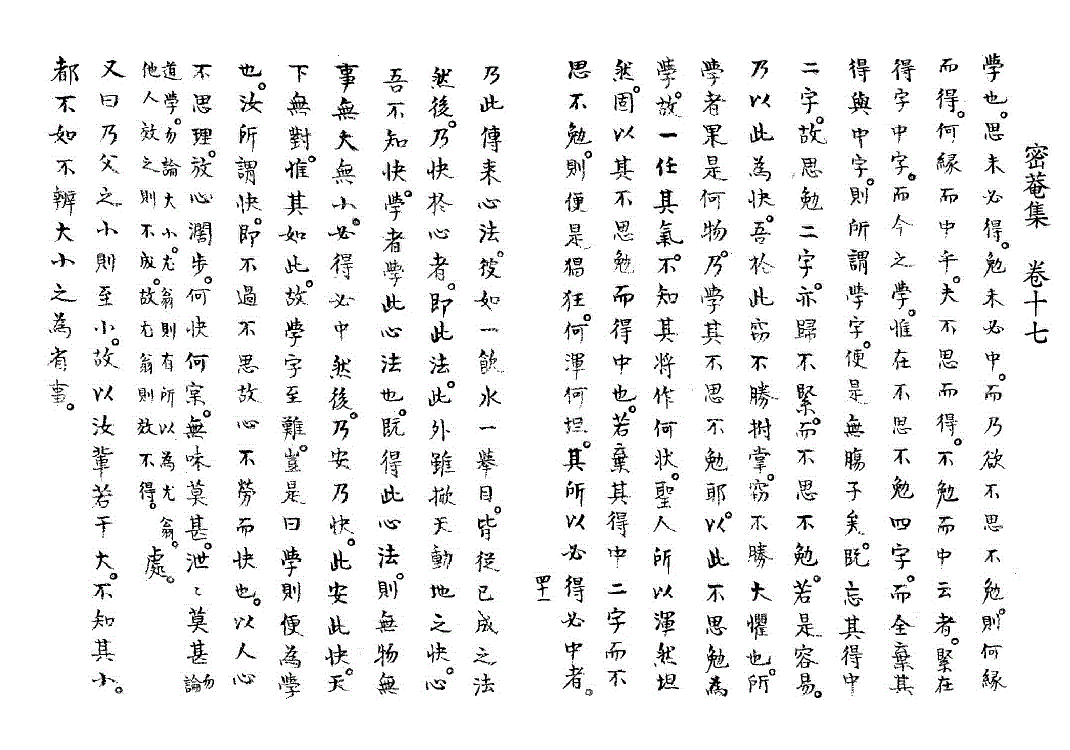 学也。思未必得。勉未必中。而乃欲不思不勉。则何缘而得。何缘而中乎。夫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云者。紧在得字中字。而今之学。惟在不思不勉四字。而全弃其得与中字。则所谓学字。便是无肠子矣。既忘其得中二字。故思勉二字。亦归不紧。而不思不勉。若是容易。乃以此为快。吾于此窃不胜拊掌。窃不胜大惧也。所学者果是何物。乃学其不思不勉耶。以此不思勉为学。故一任其气。不知其将作何状。圣人所以浑然坦然。固以其不思勉而得中也。若弃其得中二字而不思不勉。则便是猖狂。何浑何坦。其所以必得必中者。乃此传来心法。彼如一饮水一举目。皆从已成之法然后。乃快于心者。即此法。此外虽掀天动地之快。心吾不知快。学者学此心法也。既得此心法。则无物无事无大无小。必得必中然后。乃安乃快。此安此快。天下无对。惟其如此。故学字至难。岂是曰学则便为学也。汝所谓快。即不过不思故心不劳而快也。以人心不思理。放心阔步。何快何宲。无味莫甚。泄泄莫甚(勿论道学。勿论大小。尤翁则有所以为尤翁。他人效之则不成。故尤翁则效不得。)处。
学也。思未必得。勉未必中。而乃欲不思不勉。则何缘而得。何缘而中乎。夫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云者。紧在得字中字。而今之学。惟在不思不勉四字。而全弃其得与中字。则所谓学字。便是无肠子矣。既忘其得中二字。故思勉二字。亦归不紧。而不思不勉。若是容易。乃以此为快。吾于此窃不胜拊掌。窃不胜大惧也。所学者果是何物。乃学其不思不勉耶。以此不思勉为学。故一任其气。不知其将作何状。圣人所以浑然坦然。固以其不思勉而得中也。若弃其得中二字而不思不勉。则便是猖狂。何浑何坦。其所以必得必中者。乃此传来心法。彼如一饮水一举目。皆从已成之法然后。乃快于心者。即此法。此外虽掀天动地之快。心吾不知快。学者学此心法也。既得此心法。则无物无事无大无小。必得必中然后。乃安乃快。此安此快。天下无对。惟其如此。故学字至难。岂是曰学则便为学也。汝所谓快。即不过不思故心不劳而快也。以人心不思理。放心阔步。何快何宲。无味莫甚。泄泄莫甚(勿论道学。勿论大小。尤翁则有所以为尤翁。他人效之则不成。故尤翁则效不得。)处。又曰乃父之小则至小。故以汝辈若干大。不知其小。都不如不辨大小之为省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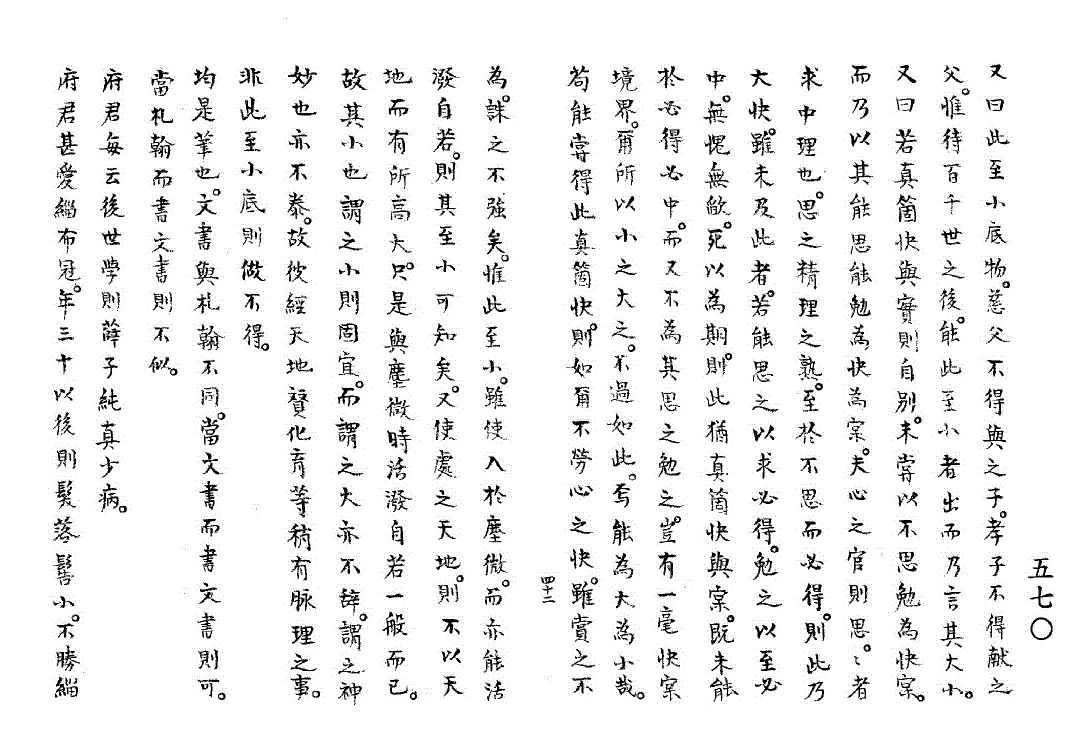 又曰此至小底物。慈父不得与之子。孝子不得献之父。惟待百千世之后。能此至小者出而乃言其大小。
又曰此至小底物。慈父不得与之子。孝子不得献之父。惟待百千世之后。能此至小者出而乃言其大小。又曰若真个快与实则自别。未尝以不思勉为快宲。而乃以其能思能勉为快为宲。夫心之官则思。思者求中理也。思之精理之熟。至于不思而必得。则此乃大快。虽未及此者。若能思之以求必得。勉之以至必中。无愧无欿。死以为期。则此犹真个快与宲。既未能于必得必中。而又不为其思之勉之。岂有一毫快宲境界。尔所以小之大之。不过如此。焉能为大为小哉。苟能尝得此真个快。则如尔不劳心之快。虽赏之不为。诛之不强矣。惟此至小。虽使入于尘微。而亦能活泼自若。则其至小可知矣。又使处之天地。则不以天地而有所高大。只是与尘微时活泼自若一般而已。故其小也谓之小则固宜。而谓之大亦不辞。谓之神妙也亦不泰。故彼经天地赞化育等稍有脉理之事。非此至小底则做不得。
均是笔也。文书与札翰不同。当文书而书文书则可。当札翰而书文书则不似。
府君每云后世学则薛子纯真少病。
府君甚爱缁布冠。年三十以后则发落髻小。不胜缁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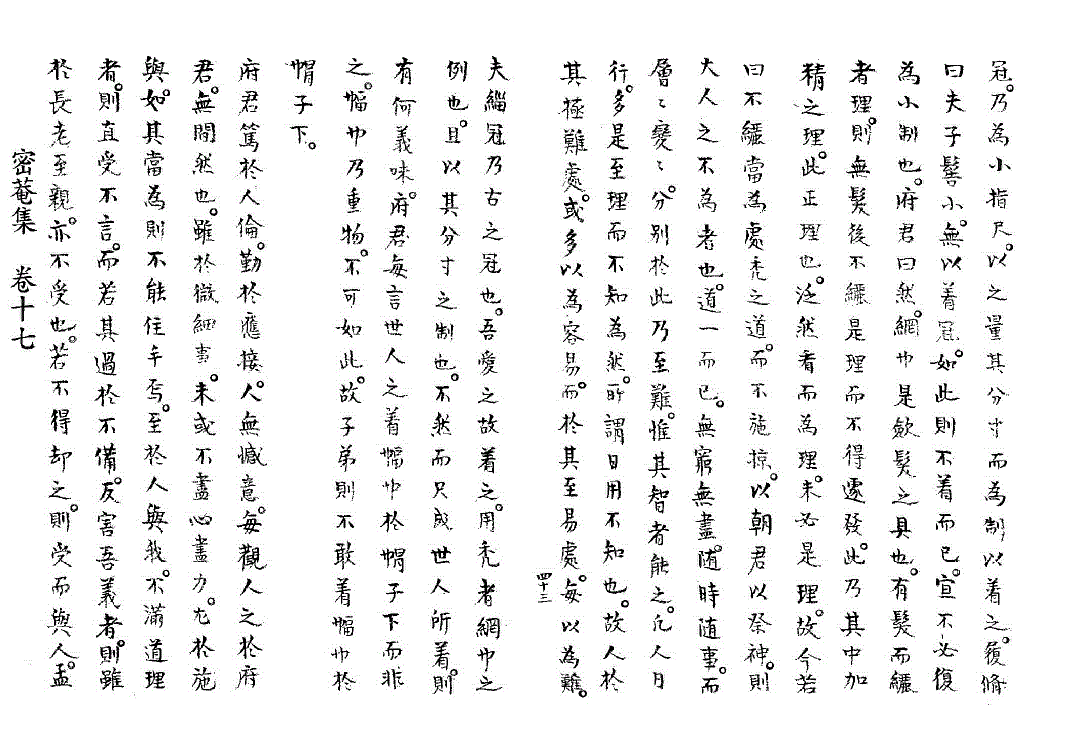 冠。乃为小指尺。以之量其分寸而为制以着之。履脩曰夫子髻小。无以着冠。如此则不着而已。宜不必复为小制也。府君曰然。网巾是敛发之具也。有发而纚者理。则无发后不纚是理而不得遽发。此乃其中加精之理。此正理也。泛然看而为理。未必是理。故今若曰不纚当为处秃之道。而不施掠。以朝君以祭神。则大人之不为者也。道一而已。无穷无尽。随时随事。而层层变变。分别于此乃至难。惟其智者能之。凡人日行。多是至理而不知为然。所谓日用不知也。故人于其极难处。或多以为容易。而于其至易处。每以为难。夫缁冠乃古之冠也。吾爱之故着之。用秃者网巾之例也。且以其分寸之制也。不然而只成世人所着。则有何义味。府君每言世人之着幅巾于帽子下而非之。幅巾乃重物。不可如此。故子弟则不敢着幅巾于帽子下。
冠。乃为小指尺。以之量其分寸而为制以着之。履脩曰夫子髻小。无以着冠。如此则不着而已。宜不必复为小制也。府君曰然。网巾是敛发之具也。有发而纚者理。则无发后不纚是理而不得遽发。此乃其中加精之理。此正理也。泛然看而为理。未必是理。故今若曰不纚当为处秃之道。而不施掠。以朝君以祭神。则大人之不为者也。道一而已。无穷无尽。随时随事。而层层变变。分别于此乃至难。惟其智者能之。凡人日行。多是至理而不知为然。所谓日用不知也。故人于其极难处。或多以为容易。而于其至易处。每以为难。夫缁冠乃古之冠也。吾爱之故着之。用秃者网巾之例也。且以其分寸之制也。不然而只成世人所着。则有何义味。府君每言世人之着幅巾于帽子下而非之。幅巾乃重物。不可如此。故子弟则不敢着幅巾于帽子下。府君笃于人伦。勤于应接。人无憾意。每观人之于府君。无间然也。虽于微细事。未或不尽心尽力。尤于施与。如其当为则不能住手焉。至于人与我。不满道理者。则直受不言。而若其过于不备。反害吾义者。则虽于长老至亲。亦不受也。若不得却之。则受而与人。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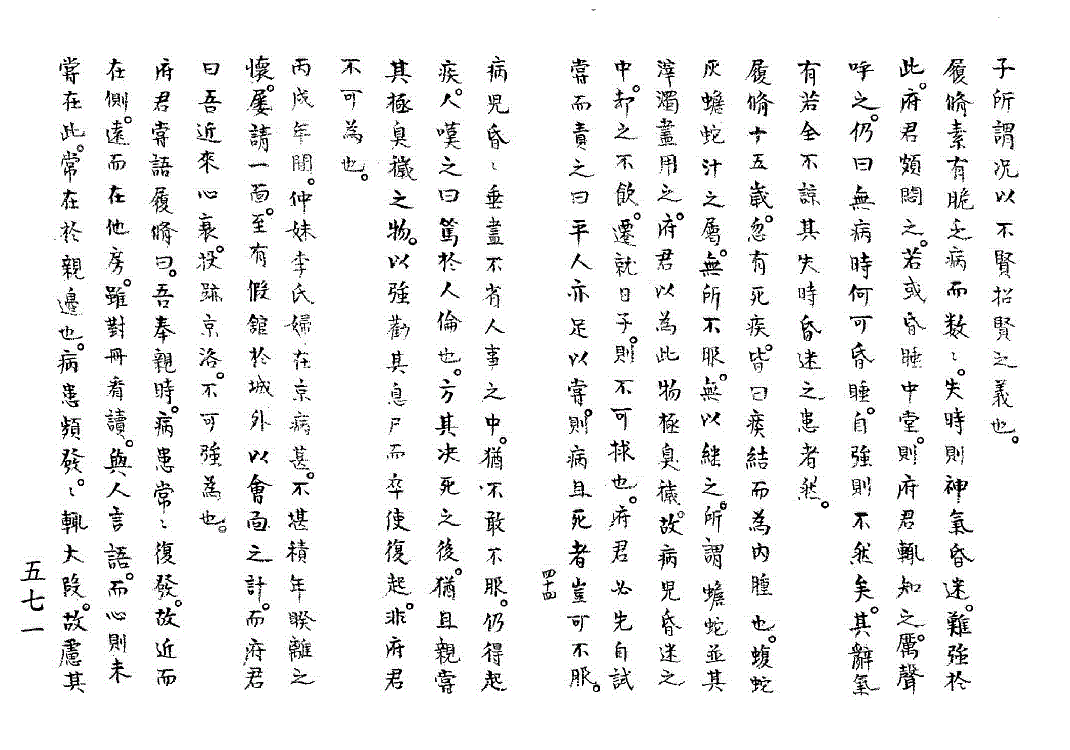 子所谓况以不贤招贤之义也。
子所谓况以不贤招贤之义也。履脩素有脆乏病而数数。失时则神气昏迷。难强于此。府君颇闷之。若或昏睡中堂。则府君辄知之。厉声呼之。仍曰无病时何可昏睡。自强则不然矣。其辞气有若全不谅其失时昏迷之患者然。
履脩十五岁。忽有死疾。皆曰痰结而为内肿也。蝮蛇灰蟾蛇汁之属。无所不服。无以继之。所谓蟾蛇并其滓浊尽用之。府君以为此物极臭秽。故病儿昏迷之中。却之不饮。迁就日子。则不可救也。府君必先自试尝而责之曰平人亦足以尝。则病且死者岂可不服。病儿昏昏垂尽不省人事之中。犹不敢不服。仍得起疾。人叹之曰笃于人伦也。方其决死之后。犹且亲尝其极臭秽之物。以强劝其息尸而卒使复起。非府君不可为也。
丙戌年间。仲妹李氏妇在京病甚。不堪积年睽离之怀。屡请一面。至有假馆于城外以会面之计。而府君曰吾近来心衰。投迹京洛。不可强为也。
府君尝语履脩曰。吾奉亲时。病患常常复发。故近而在侧。远而在他房。虽对册看读。与人言语。而心则未尝在此。常在于亲边也。病患类发。发辄大段。故虑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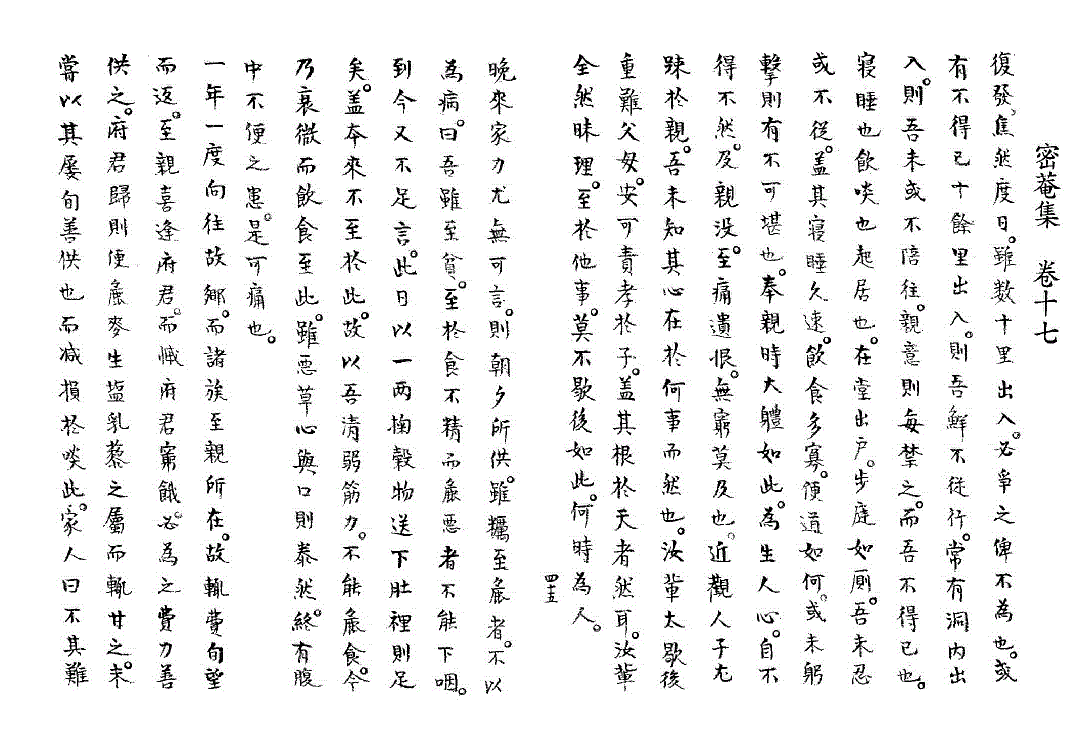 复发。焦然度日。虽数十里出入。必争之俾不为也。或有不得已十馀里出入。则吾鲜不从行。常有洞内出入。则吾未或不陪往。亲意则每禁之。而吾不得已也。寝睡也饮啖也起居也。在堂出户。步庭如厕。吾未忍或不从。盖其寝睡久速。饮食多寡。便道如何。或未躬击则有不可堪也。奉亲时大体如此。为生人心。自不得不然。及亲没。至痛遗恨。无穷莫及也。近观人子尤疏于亲。吾未知其心在于何事而然也。汝辈太歇后重难父母。安可责孝于子。盖其根于天者然耳。汝辈全然昧理。至于他事。莫不歇后如此。何时为人。
复发。焦然度日。虽数十里出入。必争之俾不为也。或有不得已十馀里出入。则吾鲜不从行。常有洞内出入。则吾未或不陪往。亲意则每禁之。而吾不得已也。寝睡也饮啖也起居也。在堂出户。步庭如厕。吾未忍或不从。盖其寝睡久速。饮食多寡。便道如何。或未躬击则有不可堪也。奉亲时大体如此。为生人心。自不得不然。及亲没。至痛遗恨。无穷莫及也。近观人子尤疏于亲。吾未知其心在于何事而然也。汝辈太歇后重难父母。安可责孝于子。盖其根于天者然耳。汝辈全然昧理。至于他事。莫不歇后如此。何时为人。晚来家力尤无可言。则朝夕所供。虽粝至粗者。不以为病。曰吾虽至贫。至于食不精而粗恶者不能下咽。到今又不足言。此日以一两掬谷物送下肚里则足矣。盖本来不至于此。故以吾清弱筋力。不能粗食。今乃衰微而饮食至此。虽恶草心与口则泰然。终有腹中不便之患。是可痛也。
一年一度向往故乡。而诸族至亲所在。故辄费旬望而返。至亲喜逢府君。而戚府君穷饿。必为之费力善供之。府君归则便粗麦生盐乳藜之属而辄甘之。未尝以其屡旬善供也而减损于啖此。家人曰不其难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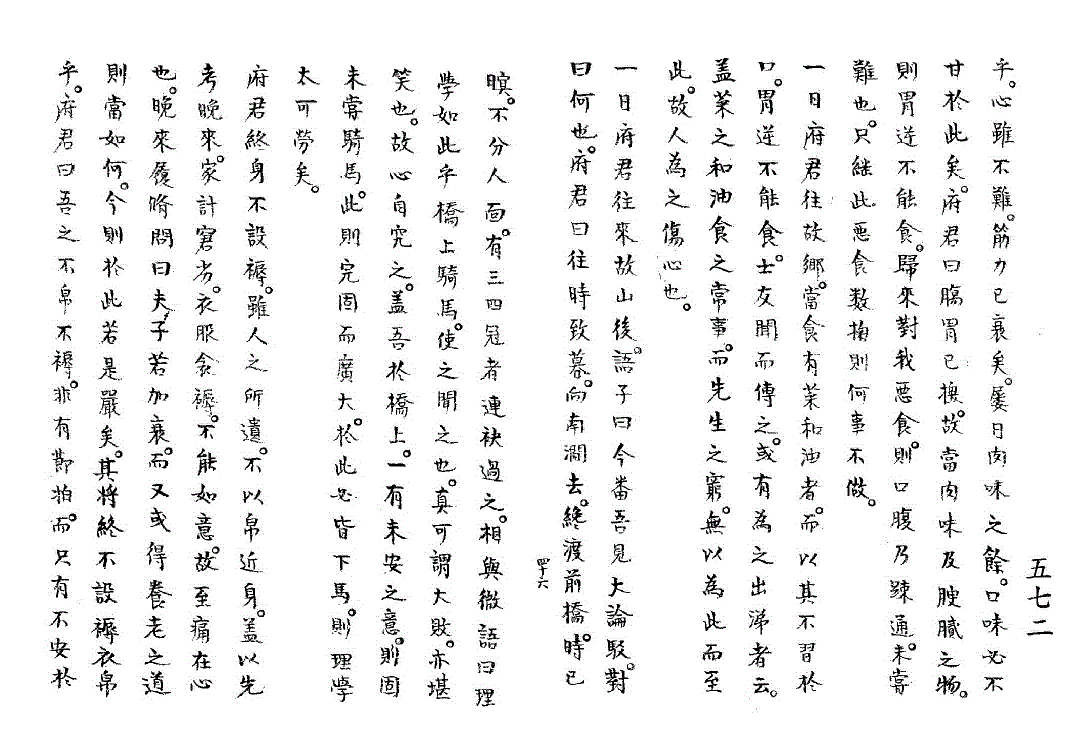 乎。心虽不难。筋力已衰矣。屡日肉味之馀。口味必不甘于此矣。府君曰肠胃已换。故当肉味及腴腻之物。则胃逆不能食。归来对我恶食。则口腹乃疏通。未尝难也。只继此恶食数掬则何事不做。
乎。心虽不难。筋力已衰矣。屡日肉味之馀。口味必不甘于此矣。府君曰肠胃已换。故当肉味及腴腻之物。则胃逆不能食。归来对我恶食。则口腹乃疏通。未尝难也。只继此恶食数掬则何事不做。一日府君往故乡。当食有菜和油者。而以其不习于口。胃逆不能食。士友闻而传之。或有为之出涕者云。盖菜之和油食之常事。而先生之穷。无以为此而至此。故人为之伤心也。
一日府君往来故山后。语子曰今番吾见大论驳。对曰何也。府君曰往时致暮。向南涧去。才渡前桥。时已暝。不分人面。有三四冠者连袂过之。相与微语曰理学如此乎桥上骑马。使之闻之也。真可谓大败。亦堪笑也。故心自究之。盖吾于桥上。一有未安之意。则固未尝骑马。此则完固而广大。于此必皆下马。则理学太可劳矣。
府君终身不设褥。虽人之所遗。不以帛近身。盖以先考晚来。家计窘劣。衣服衾褥。不能如意。故至痛在心也。晚来履脩问曰夫子若加衰。而又或得养老之道则当如何。今则于此若是严矣。其将终不设褥衣帛乎。府君曰吾之不帛不褥。非有节拍。而只有不安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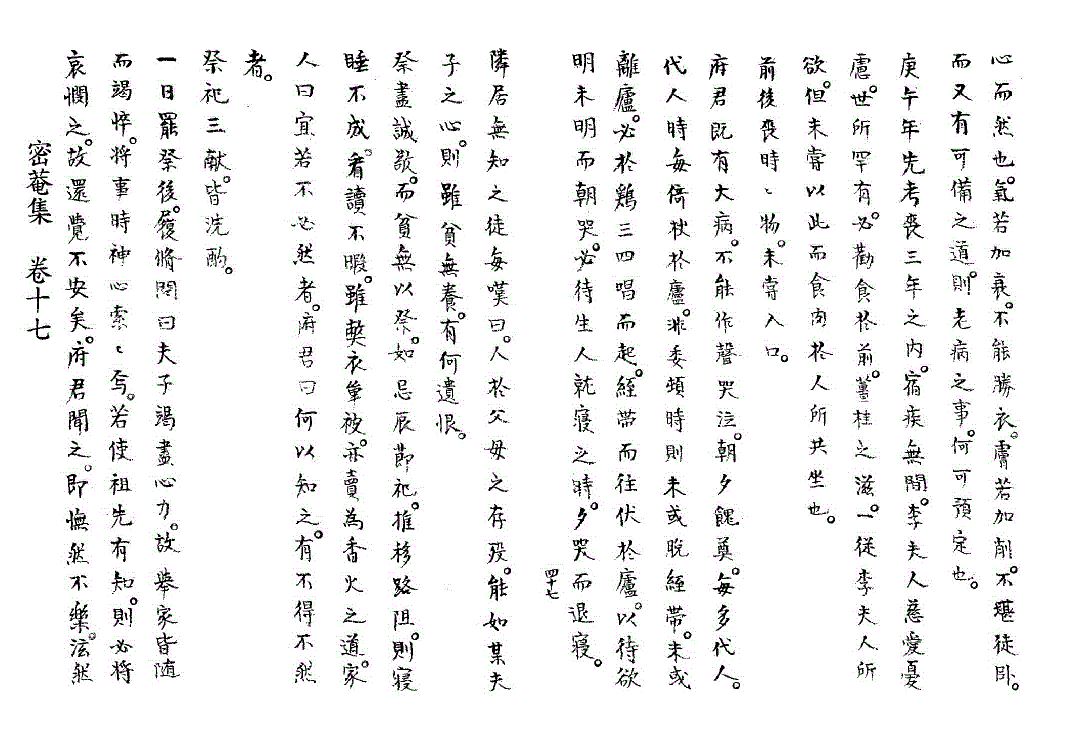 心而然也。气若加衰。不能胜衣。肤若加削。不堪徒卧。而又有可备之道。则老病之事。何可预定也。
心而然也。气若加衰。不能胜衣。肤若加削。不堪徒卧。而又有可备之道。则老病之事。何可预定也。庚午年先考丧三年之内。宿疾无间。李夫人慈爱忧虑。世所罕有。必劝食于前。姜桂之滋。一从李夫人所欲。但未尝以此而食肉于人所共坐也。
前后丧时时物。未尝入口。
府君既有大病。不能作声哭泣。朝夕馈奠。每多代人。代人时每倚杖于庐。非委顿时则未或脱绖带。未或离庐。必于鸡三四唱而起。绖带而往伏于庐。以待欲明未明而朝哭。必待生人就寝之时。夕哭而退寝。
邻居无知之徒每叹曰。人于父母之存殁。能如某夫子之心。则虽贫无养。有何遗恨。
祭尽诚敬。而贫无以祭。如忌辰节祀。推移路阻。则寝睡不成。看读不暇。虽弊衣单被。亦卖为香火之道。家人曰宜若不必然者。府君曰何以知之。有不得不然者。
祭祀三献。皆洗酌。
一日罢祭后。履脩问曰夫子竭尽心力。故举家皆随而竭悴。将事时神心索索焉。若使祖先有知。则必将哀悯之。故还觉不安矣。府君闻之。即怃然不乐。泫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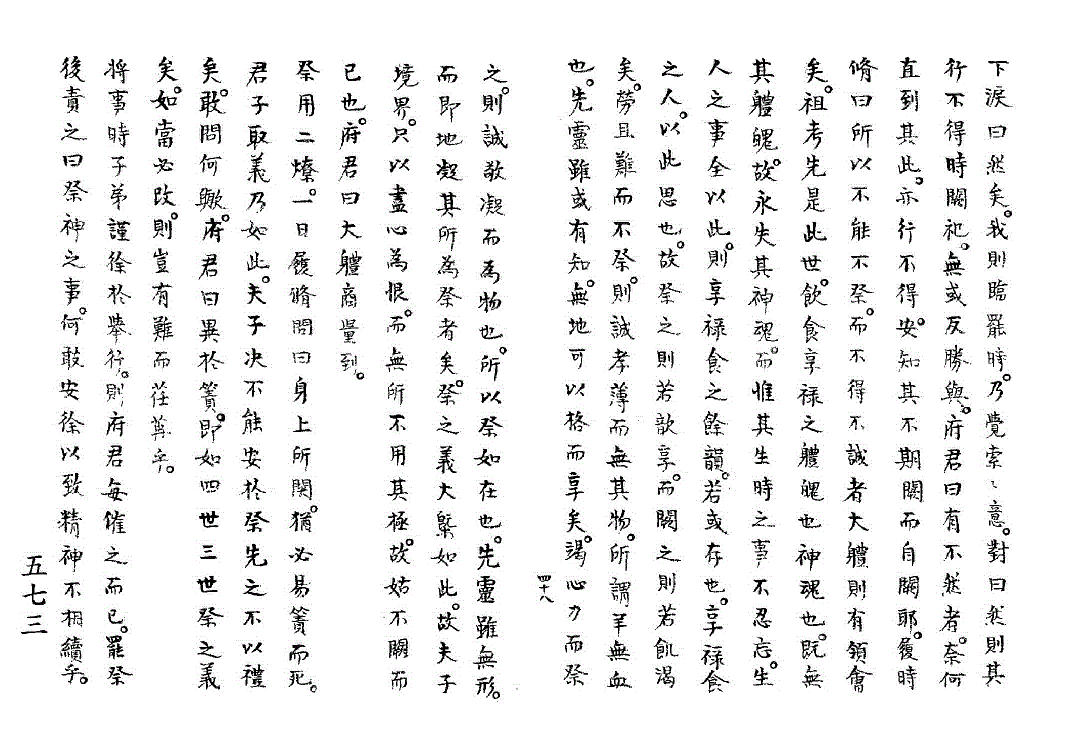 下泪曰然矣。我则临罢时。乃觉索索意。对曰然则其行不得时阙祀。无或反胜与。府君曰有不然者。奈何直到其此。亦行不得。安知其不期阙而自阙耶。履时脩曰所以不能不祭。而不得不诚者大体则有领会矣。祖考先是此世。饮食享禄之体魄也神魂也。既无其体魄。故永失其神魂。而惟其生时之事不忍忘。生人之事全以此。则享禄食之馀韵。若或存也。享禄食之人。以此思也。故祭之则若歆享。而阙之则若饥渴矣。劳且难而不祭。则诚孝薄而无其物。所谓羊无血也。先灵虽或有知。无地可以格而享矣。竭心力而祭之。则诚敬凝而为物也。所以祭如在也。先灵虽无形。而即地凝其所为祭者矣。祭之义大槩如此。故夫子境界。只以尽心为恨。而无所不用其极。故姑不阙而已也。府君曰大体商量到。
下泪曰然矣。我则临罢时。乃觉索索意。对曰然则其行不得时阙祀。无或反胜与。府君曰有不然者。奈何直到其此。亦行不得。安知其不期阙而自阙耶。履时脩曰所以不能不祭。而不得不诚者大体则有领会矣。祖考先是此世。饮食享禄之体魄也神魂也。既无其体魄。故永失其神魂。而惟其生时之事不忍忘。生人之事全以此。则享禄食之馀韵。若或存也。享禄食之人。以此思也。故祭之则若歆享。而阙之则若饥渴矣。劳且难而不祭。则诚孝薄而无其物。所谓羊无血也。先灵虽或有知。无地可以格而享矣。竭心力而祭之。则诚敬凝而为物也。所以祭如在也。先灵虽无形。而即地凝其所为祭者矣。祭之义大槩如此。故夫子境界。只以尽心为恨。而无所不用其极。故姑不阙而已也。府君曰大体商量到。祭用二燎。一日履脩问曰身上所关。犹必易箦而死。君子取义乃如此。夫子决不能安于祭先之不以礼矣。敢问何欤。府君曰异于箦。即如四世三世祭之义矣。如当必改。则岂有难而荏苒乎。
将事时子弟谨徐于举行。则府君每催之而已。罢祭后责之曰祭神之事。何敢安徐以致精神不相续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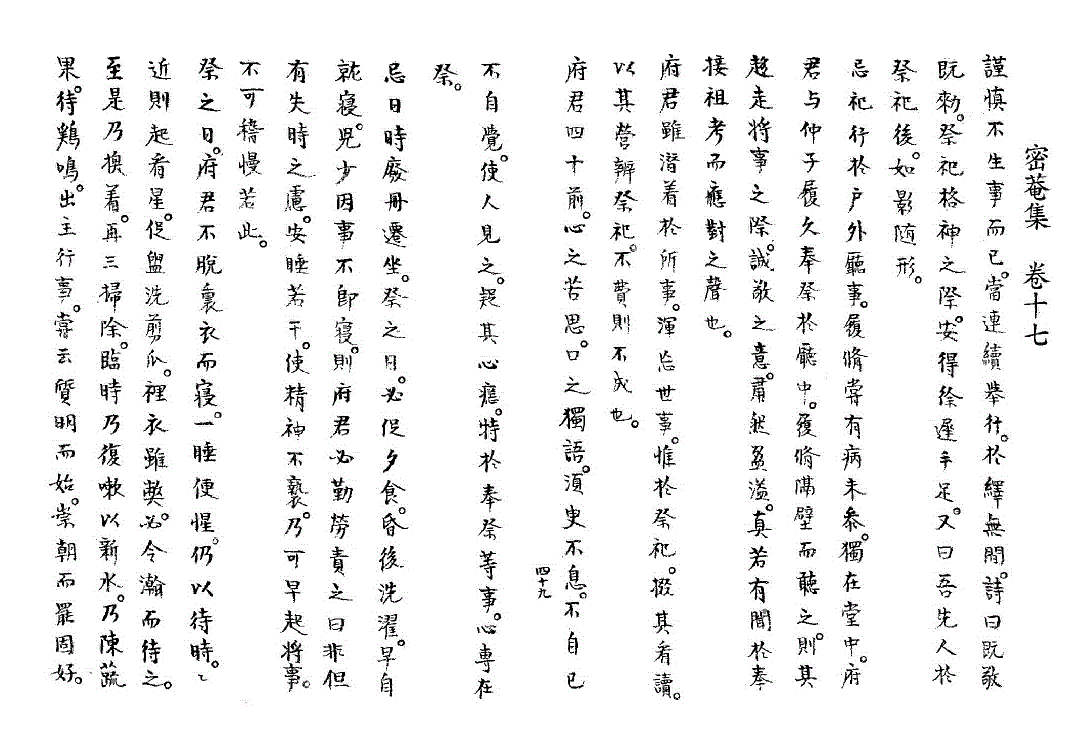 谨慎不生事而已。当连续举行。于绎无间。诗曰既敬既敕。祭祀格神之际。安得徐迟手足。又曰吾先人于祭祀后。如影随形。
谨慎不生事而已。当连续举行。于绎无间。诗曰既敬既敕。祭祀格神之际。安得徐迟手足。又曰吾先人于祭祀后。如影随形。忌祀行于户外厅事。履脩尝有病未参。独在堂中。府君与仲子履久奉祭于厅中。履脩隔壁而听之。则其趍走将事之际。诚敬之意。肃然盈溢。真若有闻于奉接祖考而应对之声也。
府君虽潜着于所事。浑忘世事。惟于祭祀。掇其看读。以其营辨祭祀。不费则不成也。
府君四十前。心之苦思。口之独语。须臾不息。不自已不自觉。使人见之。疑其心𤹂。特于奉祭等事。心专在祭。
忌日时废册迁坐。祭之日。必促夕食。昏后洗濯。早自就寝。儿少因事不即寝。则府君必勤劳责之曰非但有失时之虑。安睡若干。使精神不亵。乃可早起将事。不可稽慢若此。
祭之日。府君不脱里衣而寝。一睡便惺。仍以待时。时近则起看星。促盥洗剪爪。里衣虽弊。必令瀚而待之。至是乃换着。再三扫除。临时乃复嗽以新水。乃陈蔬果。待鸡鸣。出主行事。尝云质明而始。崇朝而罢固好。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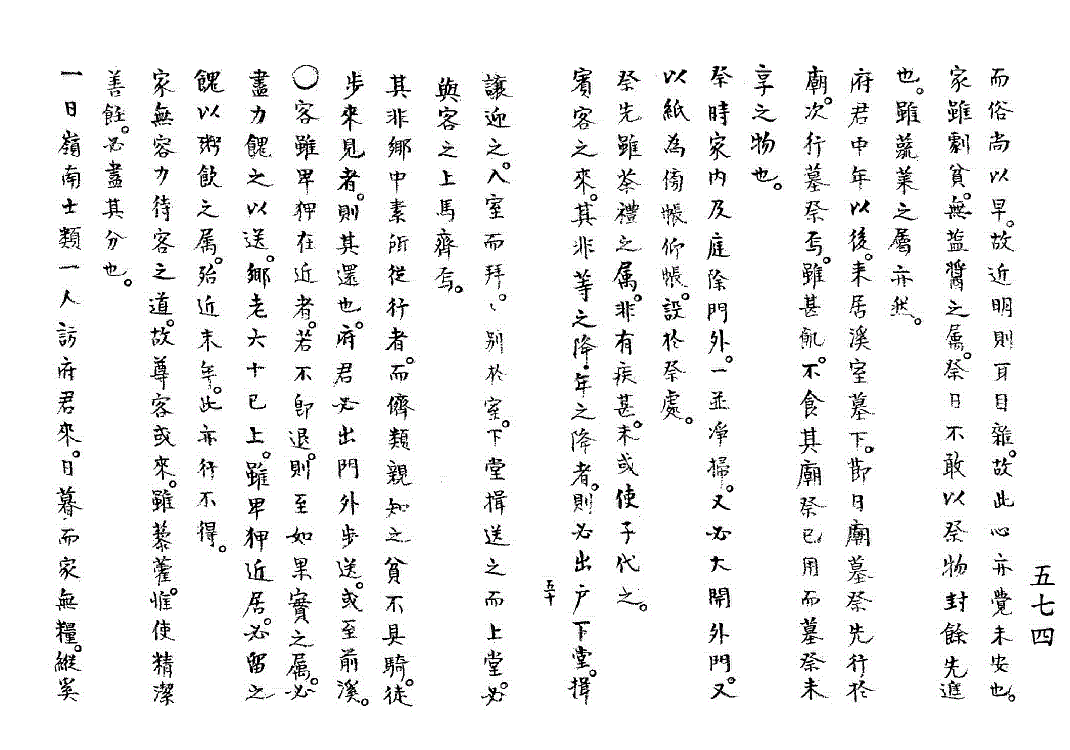 而俗尚以早。故近明则耳目杂。故此心亦觉未安也。家虽剧贫。无盐酱之属。祭日不敢以祭物封馀先进也。虽蔬菜之属亦然。
而俗尚以早。故近明则耳目杂。故此心亦觉未安也。家虽剧贫。无盐酱之属。祭日不敢以祭物封馀先进也。虽蔬菜之属亦然。府君中年以后。来居溪室墓下。节日庙墓祭先行于庙。次行墓祭焉。虽甚饥。不食其庙祭已用而墓祭未享之物也。
祭时家内及庭除门外。一并净扫。又必大开外门。又以纸为傍帐仰帐。设于祭处。
祭先虽茶礼之属。非有疾甚。未或使子代之。
宾客之来。其非等之降,年之降者。则必出户下堂。揖让迎之。入室而拜。拜别于室。下堂揖送之而上堂。必与客之上马齐焉。
其非乡中素所从行者。而侪类亲知之贫不具骑。从步来见者。则其还也。府君必出门外步送。或至前溪。
○容虽卑狎在近者。若不即退。则至如果实之属。必尽力馈之以送。乡老六十已上。虽卑狎近居。必留之馈以粥饮之属。殆近末年。此亦行不得。
家无容力待客之道。故尊客或来。虽藜藿。惟使精洁善饪。必尽其分也。
一日岭南士类一人访府君来。日暮而家无粮。纵奚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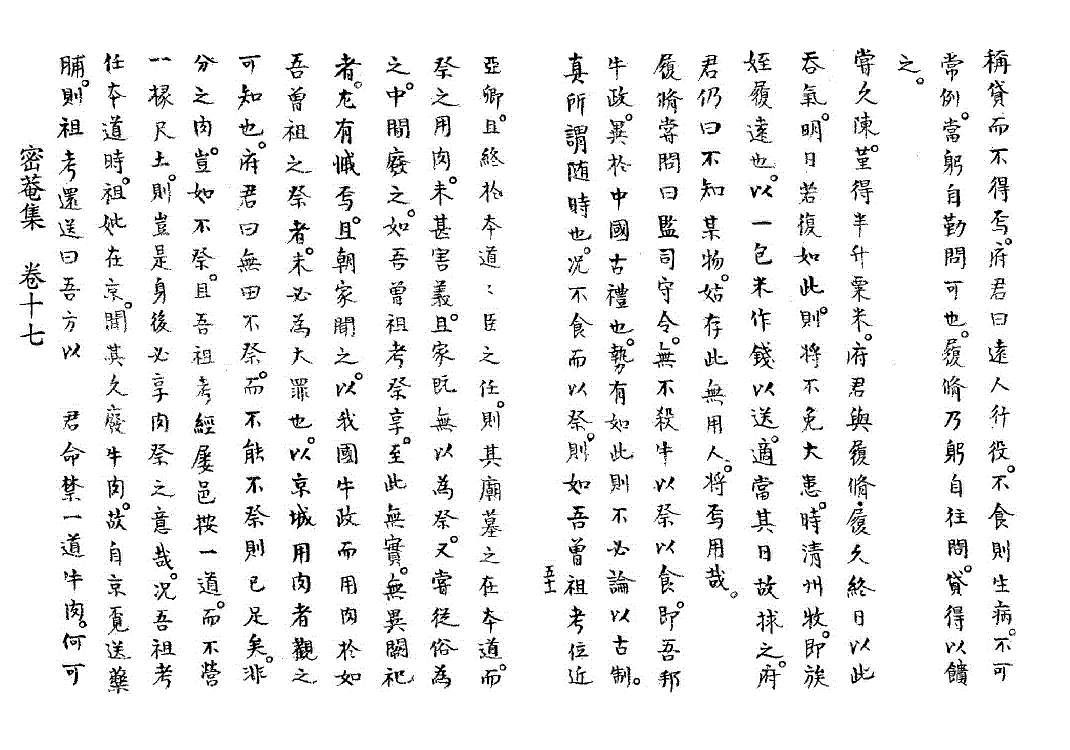 称贷而不得焉。府君曰远人行役。不食则生病。不可常例。当躬自勤问可也。履脩乃躬自往问。贷得以馈之。
称贷而不得焉。府君曰远人行役。不食则生病。不可常例。当躬自勤问可也。履脩乃躬自往问。贷得以馈之。尝久陈。堇得半升粟米。府君与履脩,履久终日以此吞气。明日若复如此。则将不免大患。时清州牧。即族侄履远也。以一包米作钱以送。适当其日故救之。府君仍曰不知某物。姑存此无用人。将焉用哉。
履脩尝问曰监司守令。无不杀牛以祭以食。即吾邦牛政。异于中国古礼也。势有如此则不必论以古制。真所谓随时也。况不食而以祭。则如吾曾祖考位近亚卿。且终于本道道臣之任。则其庙墓之在本道。而祭之用肉。未甚害义。且家既无以为祭。又尝从俗为之。中间废之。如吾曾祖考祭享。至此无实。无异阙祀者。尤有戚焉。且朝家闻之。以我国牛政而用肉于如吾曾祖之祭者。未必为大罪也。以京城用肉者观之可知也。府君曰无田不祭。而不能不祭则已足矣。非分之肉。岂如不祭。且吾祖考经屡邑按一道。而不营一椽尺土。则岂是身后必享肉祭之意哉。况吾祖考任本道时。祖妣在京。闻其久废牛肉。故自京觅送药脯。则祖考还送曰吾方以 君命禁一道牛肉。何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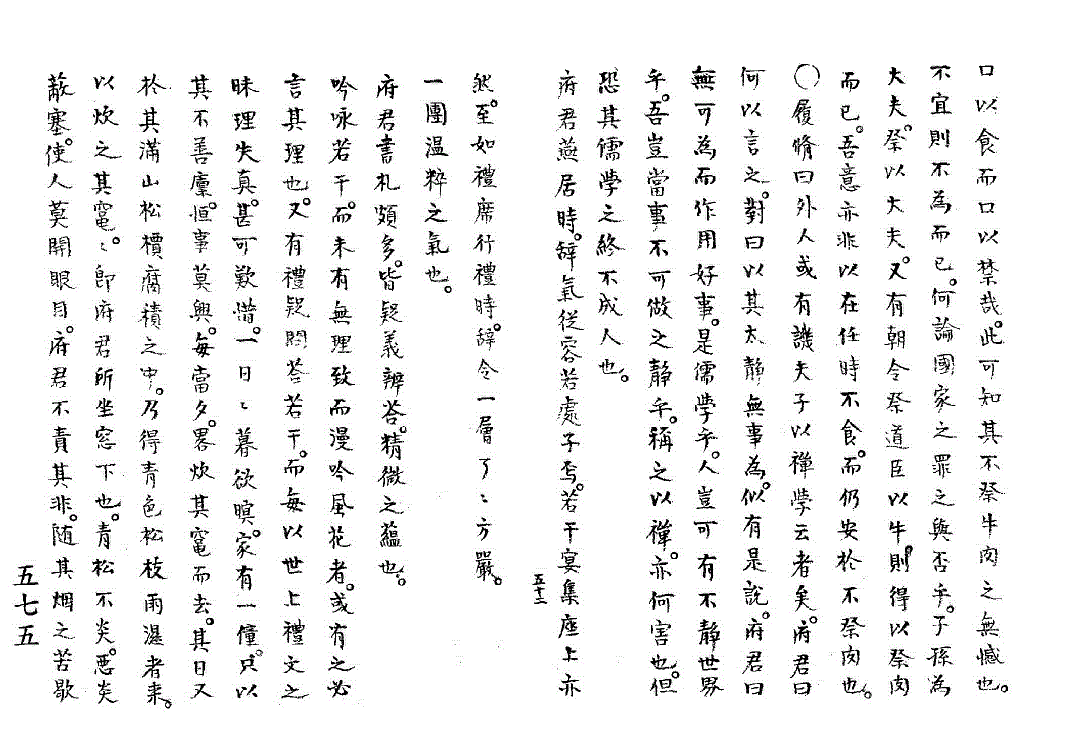 口以食而口以禁哉。此可知其不祭牛肉之无憾也。不宜则不为而已。何论国家之罪之与否乎。子孙为大夫。祭以大夫。又有朝令祭道臣以牛。则得以祭肉而已。吾意亦非以在任时不食。而仍安于不祭肉也。
口以食而口以禁哉。此可知其不祭牛肉之无憾也。不宜则不为而已。何论国家之罪之与否乎。子孙为大夫。祭以大夫。又有朝令祭道臣以牛。则得以祭肉而已。吾意亦非以在任时不食。而仍安于不祭肉也。○履脩曰外人或有讥夫子以禅学云者矣。府君曰何以言之。对曰以其太静无事为。似有是说。府君曰无可为而作用好事。是儒学乎。人岂可有不静世界乎。吾岂当事不可做之静乎。称之以禅。亦何害也。但恐其儒学之终不成人也。
府君燕居时。辞气从容若处子焉。若干宴集座上亦然。至如礼席行礼时。辞令一层了了方严。
一团温粹之气也。
府君书札颇多。皆疑义辨答。精微之蕴也。
吟咏若干。而未有无理致而漫吟风花者。或有之必言其理也。又有礼疑问答若干。而每以世上礼文之昧理失真。甚可叹惜。一日日暮欲暝。家有一僮。只以其不善廪。恒事莫兴。每当夕。略炊其灶而去。其日又于其满山松槚腐积之中。乃得青色松枝雨湿者来。以炊之其灶。灶即府君所坐窗下也。青松不炎。恶炎蔽塞。使人莫开眼目。府君不责其非。随其烟之苦歇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6H 页
 而或掩或开其窗。又有沈吟之意。履脩方步庭下。见万壑云生。山雨暮歇。茅屋低垂。青草没庭。又有好童吹烟。使不可堪。人所不乐者。而府君独无介于心。随烟掩门。悠然静坐沈吟。忽若有觉乎夫子心界。乃进窗下仰告曰苦乐劳逸。莫不自适。此所以忘饥渴之切己。忘年岁之不足欤。府君方掩门。仍即半开而强应之。仍即复沉吟焉。后来考之。廊中何事有。勤苦野人偏之句。似是其时吟者。
而或掩或开其窗。又有沈吟之意。履脩方步庭下。见万壑云生。山雨暮歇。茅屋低垂。青草没庭。又有好童吹烟。使不可堪。人所不乐者。而府君独无介于心。随烟掩门。悠然静坐沈吟。忽若有觉乎夫子心界。乃进窗下仰告曰苦乐劳逸。莫不自适。此所以忘饥渴之切己。忘年岁之不足欤。府君方掩门。仍即半开而强应之。仍即复沉吟焉。后来考之。廊中何事有。勤苦野人偏之句。似是其时吟者。府君晚来着葛丝濂溪冠。每于就寝枕上。犹不脱也。履脩问曰葛冠以胶为之。就寝犹着则易于伤弊。府君曰果然矣。履脩复曰然则枕上则勿着而脱置何如。府君曰岂其然乎。对曰此则似有妙理。盖寝时异于起时。故身亦脱衣而卧矣。冠乃起坐后所当着。身既赤脱而卧。首已安于枕上。则其必着冠。似未必稳枕上之义。似当免冠也。未知何如。府君曰吁。岂其然字。对越上帝。非特坐时为然。寝时何必有脱巾之义。虽曰身已赤脱。而尚有衾之加矣。何尝赤脱露体而卧乎。故若有寝时可着之物。则换着可而已。未尝有以寝之故而免冠之义矣。履脩曰虽然彼葛冠。若终不脱于寝时。必然不久伤破。合有变通。府君曰我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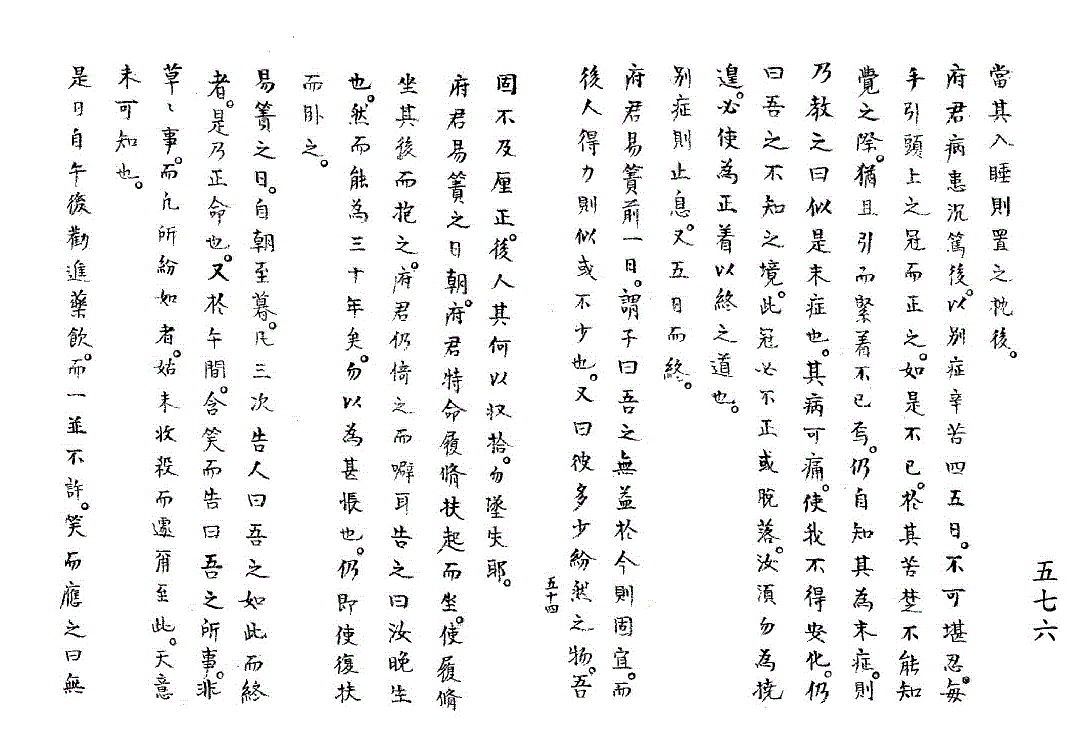 当其入睡则置之枕后。
当其入睡则置之枕后。府君病患沉笃后。以别症辛苦四五日。不可堪忍。每手引头上之冠而正之。如是不已。于其苦楚不能知觉之际。犹且引而紧着不已焉。仍自知其为末症。则乃教之曰似是末症也。其病可痛。使我不得安化。仍曰吾之不知之境。此冠必不正或脱落。汝须勿为挠遑。必使为正着以终之道也。
别症则止息。又五日而终。
府君易箦前一日。谓子曰吾之无益于今则固宜。而后人得力则似或不少也。又曰彼多少纷然之物。吾固不及厘正。后人其何以收拾。勿坠失耶。
府君易箦之日朝。府君特命履脩扶起而坐。使履脩坐其后而抱之。府君仍倚之而噼耳告之曰汝晚生也。然而能为三十年矣。勿以为甚怅也。仍即使复扶而卧之。
易箦之日。自朝至暮。凡三次告人曰吾之如此而终者。是乃正命也。又于午间。含笑而告曰吾之所事。非草草事。而凡所纷如者。姑未收杀而遽尔至此。天意未可知也。
是日自午后劝进药饮。而一并不许。笑而应之曰无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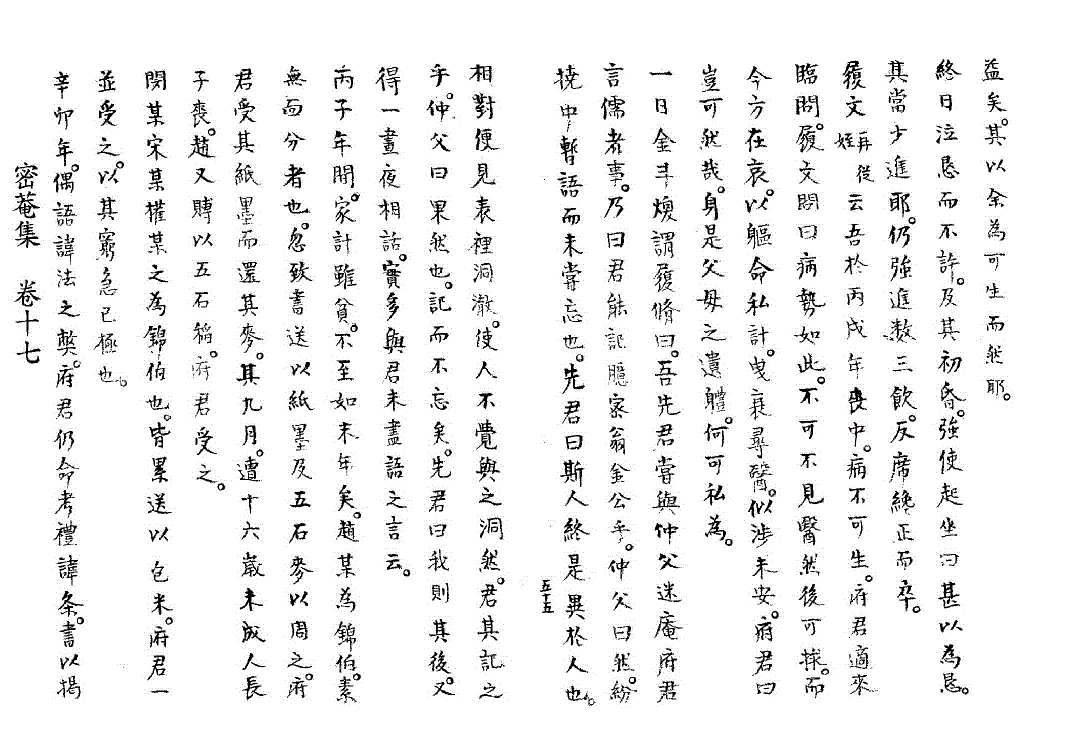 益矣。其以余为可生而然耶。
益矣。其以余为可生而然耶。终日泣恳而不许。及其初昏。强使起坐曰甚以为恳。其当少进耶。仍强进数三饮。反席才正而卒。
履文(再从侄)云吾于丙戌年丧中。病不可生。府君适来临问。履文问曰病势如此。不可不见医然后可救。而今方在哀。以躯命私计。曳衰寻医。似涉未安。府君曰岂可然哉。身是父母之遗体。何可私为。
一日金斗焕谓履脩曰。吾先君尝与仲父迷庵府君言儒者事。乃曰君能记臆密翁金公乎。仲父曰然。纷挠中暂语而未尝忘也。先君曰斯人终是异于人也。相对便见表里洞澈。使人不觉与之洞然。君其记之乎。仲父曰果然也。记而不忘矣。先君曰我则其后。又得一昼夜相话。实多与君未尽语之言云。
丙子年间。家计虽贫。不至如末年矣。赵某为锦伯。素无面分者也。忽致书送以纸墨及五石麦以周之。府君受其纸墨而还其麦。其九月。遭十六岁未成人长子丧。赵又赙以五石稻。府君受之。
闵某宋某权某之为锦伯也。皆累送以包米。府君一并受之。以其穷急已极也。
辛卯年。偶语讳法之弊。府君仍命考礼讳条。书以揭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第 5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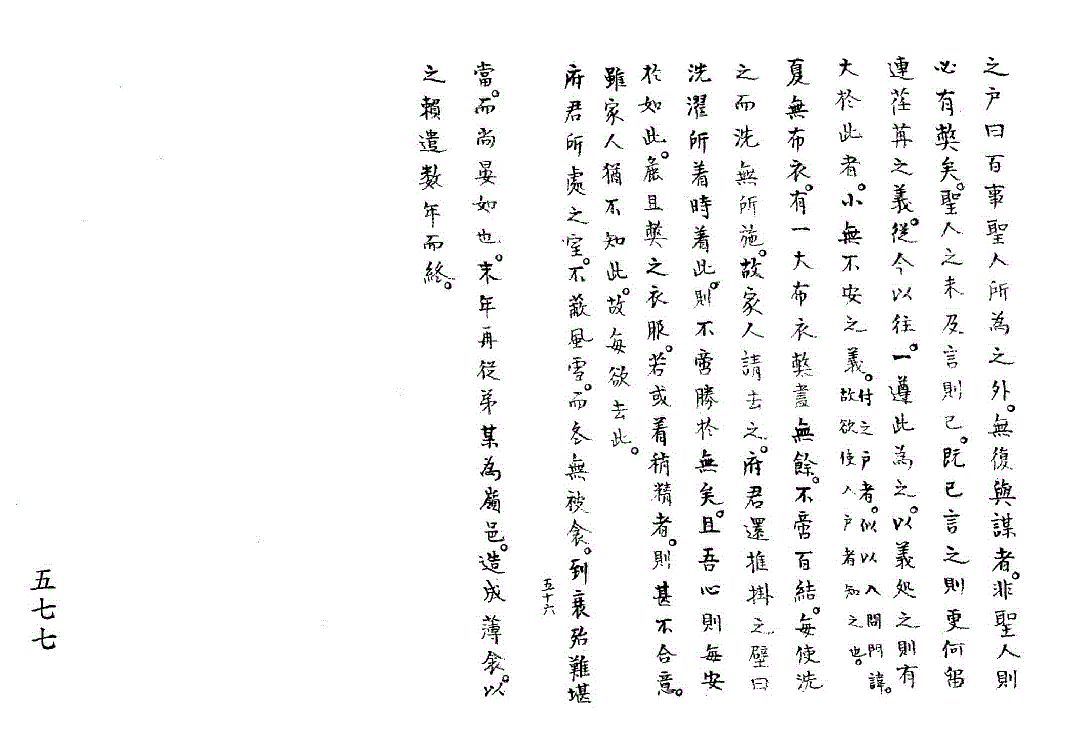 之户曰百事圣人所为之外。无复与谋者。非圣人则必有弊矣。圣人之未及言则已。既已言之则更何留连荏苒之义。从今以往。一遵此为之。以义处之则有大于此者。小无不安之义。(付之户者。似以入问门讳。故欲使入户者知之也。)
之户曰百事圣人所为之外。无复与谋者。非圣人则必有弊矣。圣人之未及言则已。既已言之则更何留连荏苒之义。从今以往。一遵此为之。以义处之则有大于此者。小无不安之义。(付之户者。似以入问门讳。故欲使入户者知之也。)夏无布衣。有一大布衣弊尽无馀。不啻百结。每使洗之而洗无所施。故家人请去之。府君还推挂之壁曰洗濯所着时着此。则不啻胜于无矣。且吾心则每安于如此。粗且弊之衣服。若或着稍精者。则甚不合意。虽家人犹不知此。故每欲去此。
府君所处之室。不蔽风雪。而冬无被衾。到衰殆难堪当。而尚晏如也。末年再从弟某为岭邑。造成薄衾。以之赖遣数年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