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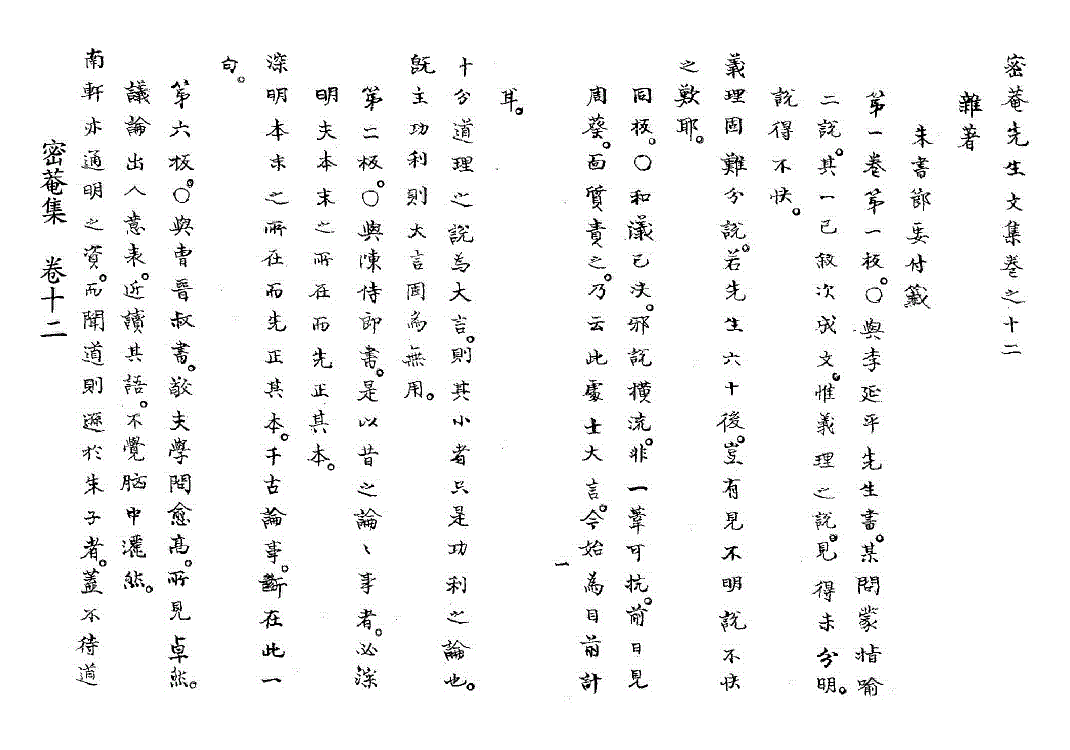 朱书节要付签
朱书节要付签第一卷第一板○与李延平先生书。某问蒙指喻二说。其一已叙次成文。惟义理之说。见得未分明。说得不快。
义理固难分说。若先生六十后。岂有见不明说不快之叹耶。
同板○和议已决。邪说横流。非一苇可抗。前日见周葵。面质责之。乃云此处士大言。今始为目前计耳。
十分道理之说为大言。则其小者只是功利之论也。既主功利则大言固为无用。
第二板○与陈侍郎书。是以昔之论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
深明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千古论事。断在此一句。
第六板○与曹晋叔书。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不觉胸中洒然。
南轩亦通明之资。而闻道则逊于朱子者。盖不待道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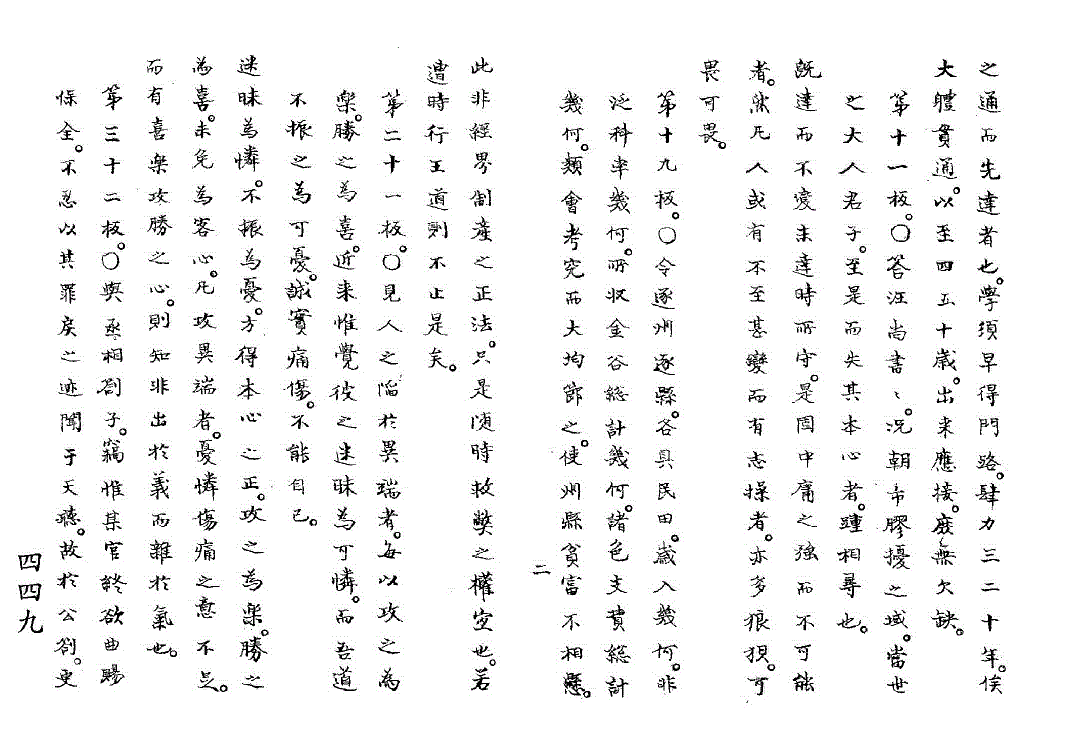 之通而先达者也。学须早得门路。肆力三二十年。俟大体贯通。以至四五十岁。出来应接。庶无欠缺。
之通而先达者也。学须早得门路。肆力三二十年。俟大体贯通。以至四五十岁。出来应接。庶无欠缺。第十一板○答汪尚书书。况朝市胶扰之域。当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寻也。
既达而不变未达时所守。是固中庸之强而不可能者。然凡人或有不至甚变而有志操者。亦多狼狈。可畏可畏。
第十九板○令逐州逐县。各具民田。岁入几何。非泛科率几何。所收金谷总计几何。诸色支费总计几何。类会考究而大均节之。使州县贫富不相悬。
此非经界制产之正法。只是随时救弊之权宜也。若遭时行王道则不止是矣。
第二十一板○见人之陷于异端者。每以攻之为乐。胜之为喜。近来惟觉彼之迷昧为可怜。而吾道不振之为可忧。诚实痛伤。不能自已。
迷昧为怜。不振为忧。方得本心之正。攻之为乐。胜之为喜。未免为客心。凡攻异端者。忧怜伤痛之意不足。而有喜乐攻胜之心。则知非出于义而杂于气也。
第三十二板○与丞相劄子。窃惟某官终欲曲赐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迹闻于天听。故于公劄。更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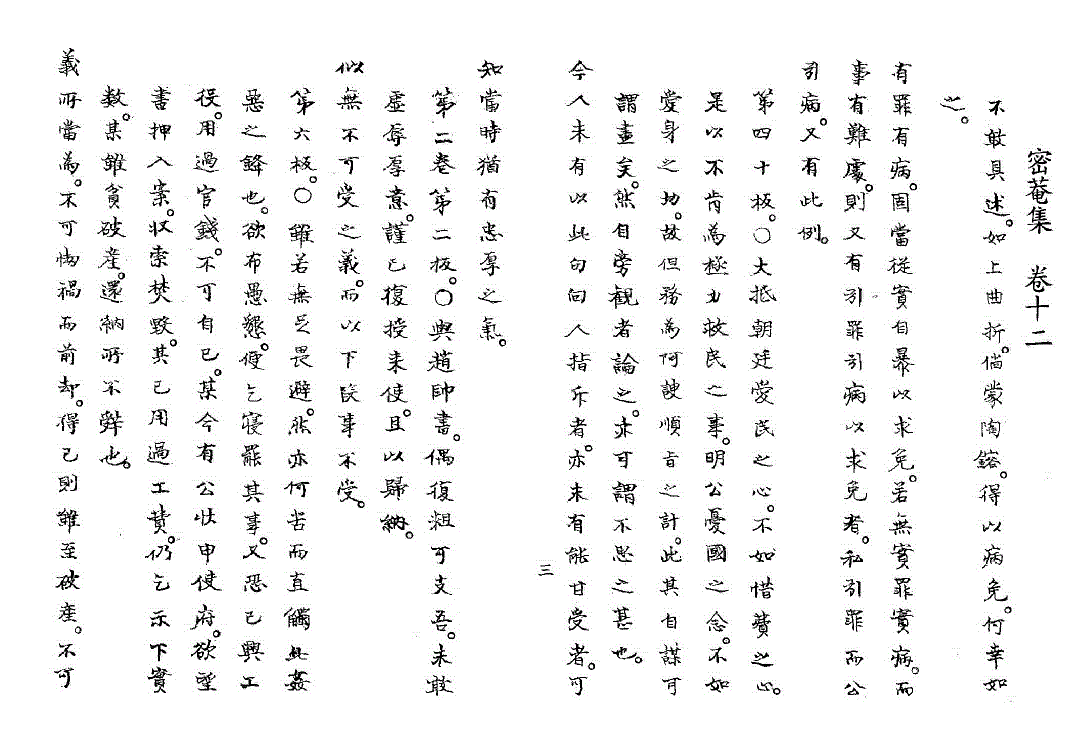 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倘蒙陶镕。得以病免。何幸如之。
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倘蒙陶镕。得以病免。何幸如之。有罪有病。固当从实自暴以求免。若无实罪实病。而事有难处。则又有引罪引病以求免者。私引罪而公引病。又有此例。
第四十板○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心。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故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者论之。亦可谓不思之甚也。
今人未有以此句向人指斥者。亦未有能甘受者。可知当时犹有忠厚之气。
第二卷第二板○与赵帅书。偶复粗可支吾。未敢虚辱厚意。谨已复授来使。且以归纳。
似无不可受之义。而以下段事不受。
第六板○虽若无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触此奸恶之锋也。欲布愚恳。便乞寝罢其事。又恐已兴工役。用过官钱。不可自已。某今有公状申使府。欲望书押入案。收索焚毁。其已用过工费。仍乞示下实数。某虽贫破产。还纳所不辞也。
义所当为。不可㥘祸而前却。得已则虽至破产。不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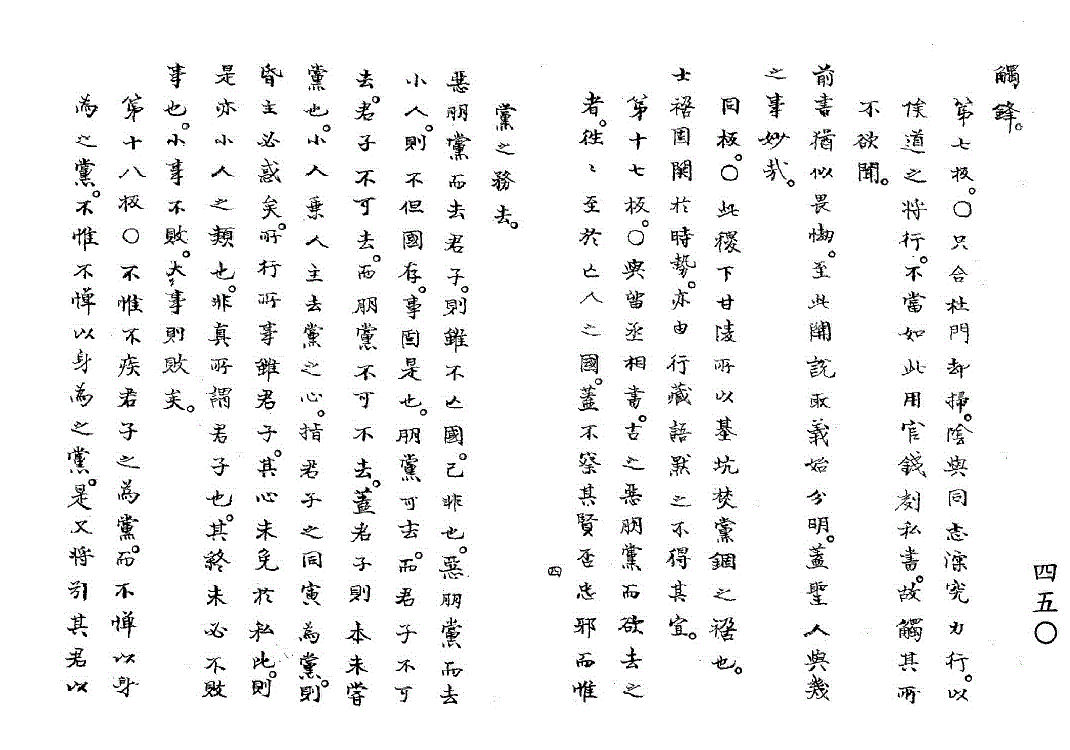 触锋。
触锋。第七板○只合杜门却扫。阴与同志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将行。不当如此用官钱刻私书。故触其所不欲闻。
前书犹似畏㥘。至此开说取义始分明。盖圣人与几之事妙哉。
同板○此稷下甘陵所以基坑焚党锢之𥚁也。
士𥚁固关于时势。亦由行藏语默之不得其宜。
第十七板○与留丞相书。古之恶朋党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亡人之国。盖不察其贤否忠邪而惟党之务去。
恶朋党而去君子。则虽不亡国。已非也。恶朋党而去小人。则不但国存。事固是也。朋党可去。而君子不可去。君子不可去。而朋党不可不去。盖君子则本未尝党也。小人乘人主去党之心。指君子之同寅为党。则昏主必惑矣。所行所事虽君子。其心未免于私比。则是亦小人之类也。非真所谓君子也。其终未必不败事也。小事不败。大事则败矣。
第十八板○不惟不疾君子之为党。而不惮以身为之党。不惟不惮以身为之党。是又将引其君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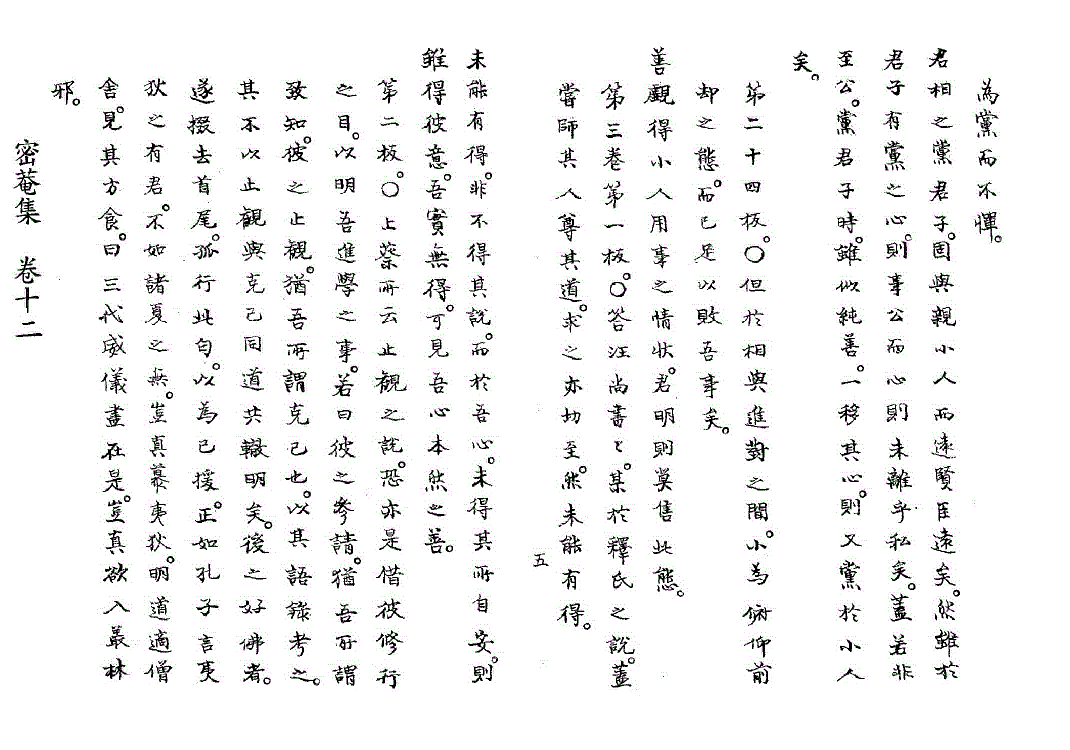 为党而不惮。
为党而不惮。君相之党君子。固与亲小人而远贤臣远矣。然虽于君子有党之心。则事公而心则未离乎私矣。盖若非至公。党君子时。虽似纯善。一移其心。则又党于小人矣。
第二十四板○但于相与进对之间。小为俯仰前却之态。而已足以败吾事矣。
善觑得小人用事之情状。君明则莫售此态。
第三卷第一板○答汪尚书书。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然未能有得。
未能有得。非不得其说。而于吾心。未得其所自安。则虽得彼意。吾实无得。可见吾心本然之善。
第二板○上蔡所云止观之说。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进学之事。若曰彼之参请。犹吾所谓致知。彼之止观。犹吾所谓克己也。以其语录考之。其不以止观与克己同道共辙明矣。后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为己援。正如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岂真慕夷狄。明道适僧舍。见其方食。曰三代威仪尽在是。岂真欲入丛林邪。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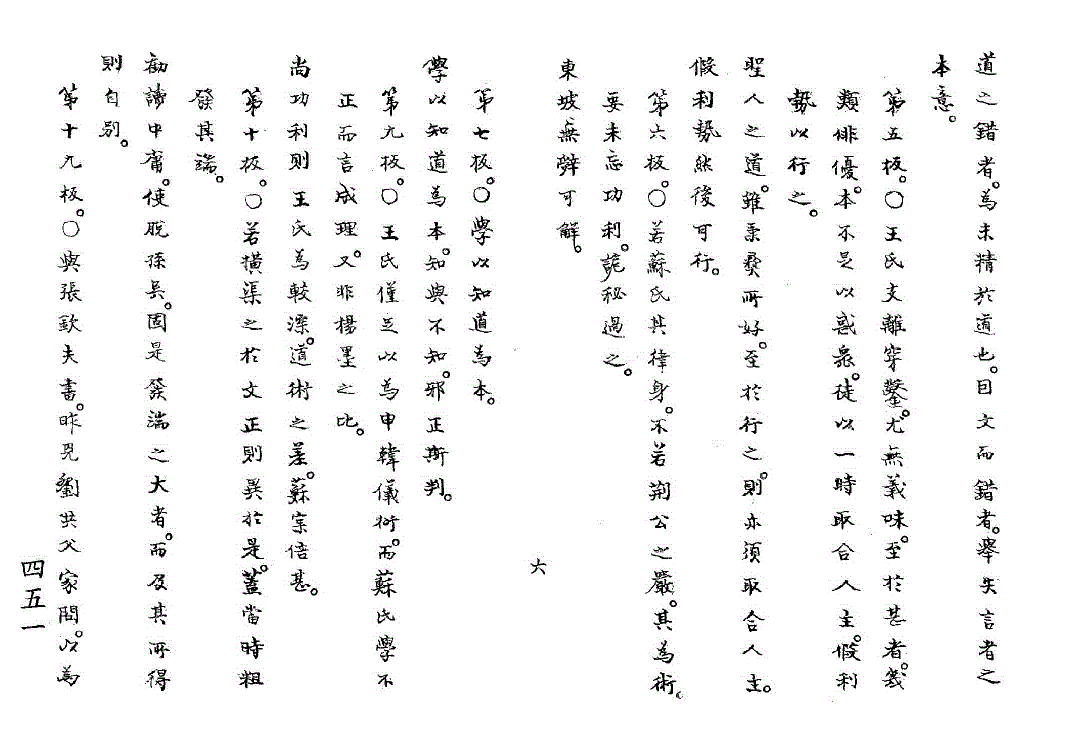 道之错者。为未精于道也。因文而错者。举失言者之本意。
道之错者。为未精于道也。因文而错者。举失言者之本意。第五板○王氏支离穿凿。尤无义味。至于甚者。几类俳优。本不足以惑众。徒以一时取合人主。假利势以行之。
圣人之道。虽秉彝所好。至于行之。则亦须取合人主。假利势然后可行。
第六板○若苏氏其律身。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诡秘过之。
东坡无辞可解。
第七板○学以知道为本。
学以知道为本。知与不知。邪正斯判。
第九板○王氏仅足以为申韩仪衍。而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
尚功利则王氏为较深。道术之差。苏宲倍甚。
第十板○若横渠之于文正则异于是。盖当时粗发其端。
劝读中庸。使脱孙吴。固是发端之大者。而及其所得则自别。
第十九板○与张钦夫书。昨见刘共父家问。以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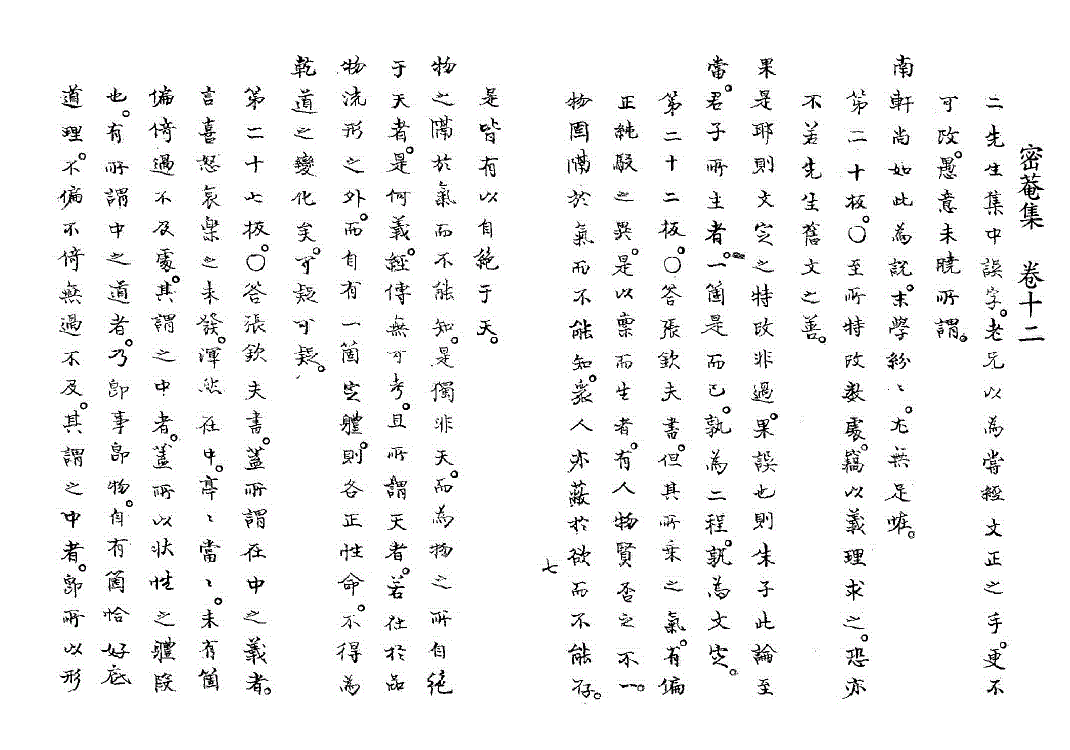 二先生集中误字。老兄以为尝经文正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晓所谓。
二先生集中误字。老兄以为尝经文正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晓所谓。南轩尚如此为说。末学纷纷。尤无足怪。
第二十板○至所特改数处。窃以义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旧文之善。
果是耶则文定之特改非过。果误也则朱子此论至当。君子所主者。一个是而已。孰为二程。孰为文定。
第二十二板○答张钦夫书。但其所乘之气。有偏正纯驳之异。是以禀而生者。有人物贤否之不一。物固隔于气而不能知。众人亦蔽于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绝于天。
物之隔于气而不能知。是独非天。而为物之所自绝于天者。是何义。经传无可考。且所谓天者。若在于品物流形之外。而自有一个定体。则各正性命。不得为乾道之变化矣。可疑可疑。
第二十七板○答张钦夫书。盖所谓在中之义者。言喜怒哀乐之未发。浑然在中。亭亭当当。未有个偏倚过不及处。其谓之中者。盖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有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其谓之中者。即所以形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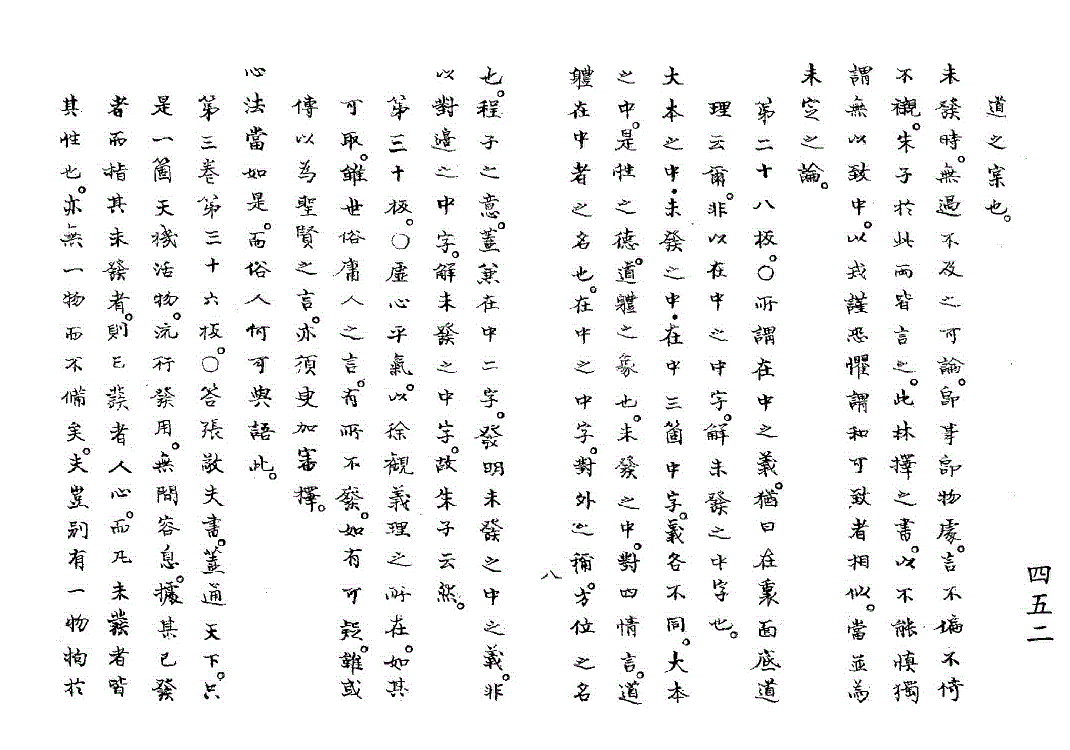 道之宲也。
道之宲也。未发时。无过不及之可论。即事即物处。言不偏不倚不衬。朱子于此两皆言之。此林择之书。以不能慎独谓无以致中。以戒谨恐惧谓和可致者相似。当并为未定之论。
第二十八板○所谓在中之义。犹曰在里面底道理云尔。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发之中字也。
大本之中,未发之中,在中三个中字。义各不同。大本之中。是性之德。道体之象也。未发之中。对四情言。道体在中者之名也。在中之中字。对外之称。方位之名也。程子之意。盖兼在中二字。发明未发之中之义。非以对边之中字。解未发之中字。故朱子云然。
第三十板○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臾加审择。
心法当如是。而俗人何可与语此。
第三卷第三十六板○答张敬夫书。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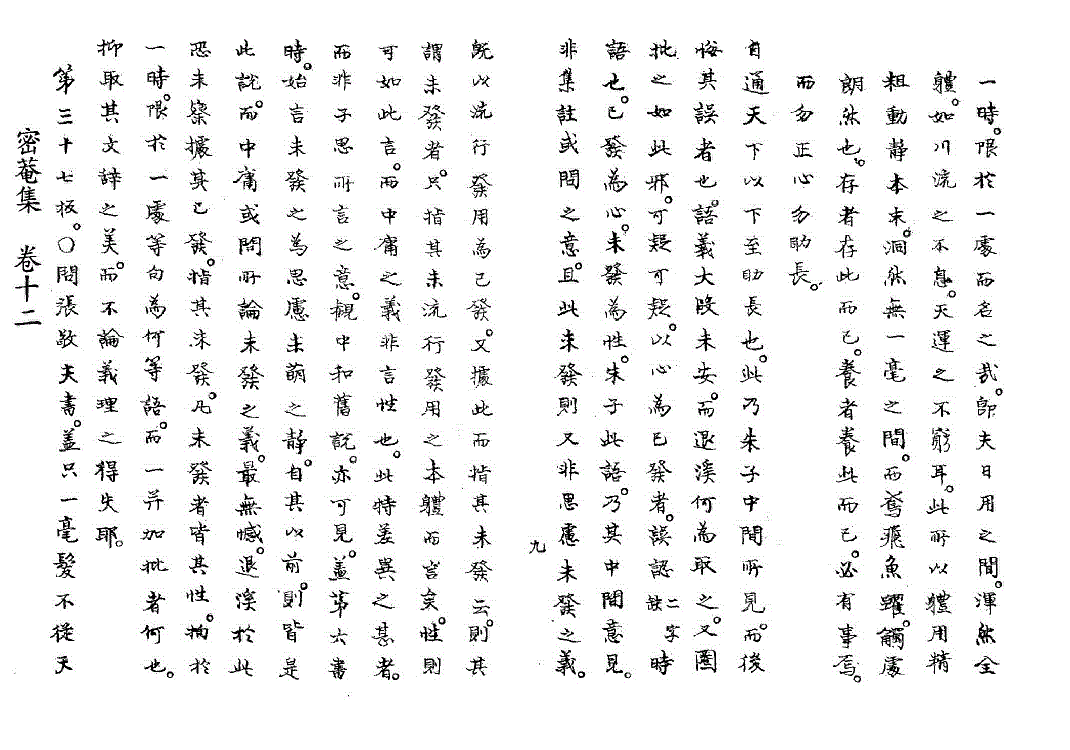 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助长。
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助长。自通天下以下至助长也。此乃朱子中间所见。而后悔其误者也。语义大段未安。而退溪何为取之。又圈批之如此邪。可疑可疑。以心为已发者。误认(二字缺)时语也。已发为心。未发为性。朱子此语。乃其中间意见。非集注或问之意。且此未发则又非思虑未发之义。既以流行发用为已发。又据此而指其未发云。则其谓未发者。只指其未流行发用之本体而言矣。性则可如此言。而中庸之义非言性也。此特差异之甚者。而非子思所言之意。观中和旧说。亦可见。盖第六书时。始言未发之为思虑未萌之静。自其以前。则皆是此说。而中庸或问所论未发之义。最无憾。退溪于此恐未察据其已发。指其未发。凡未发者皆其性。拘于一时。限于一处等句为何等语。而一并加批者何也。抑取其文辞之美。而不论义理之得失耶。
第三十七板○问张敬夫书。盖只一毫发不从天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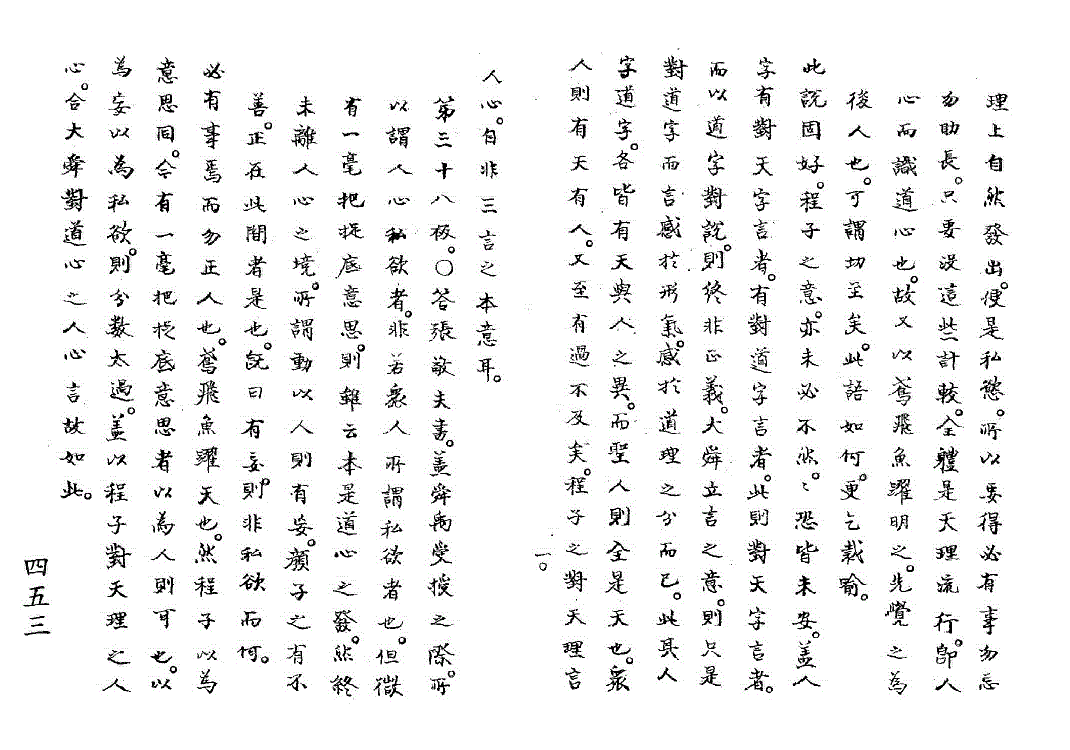 理上自然发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勿忘勿助长。只要没这些计较。全体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识道心也。故又以鸢飞鱼跃明之。先觉之为后人也。可谓切至矣。此语如何。更乞裁喻。
理上自然发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勿忘勿助长。只要没这些计较。全体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识道心也。故又以鸢飞鱼跃明之。先觉之为后人也。可谓切至矣。此语如何。更乞裁喻。此说固好。程子之意。亦未必不然。然恐皆未安。盖人字有对天字言者。有对道字言者。此则对天字言者。而以道字对说。则终非正义。大舜立言之意。则只是对道字而言感于形气。感于道理之分而已。此其人字道字。各皆有天与人之异。而圣人则全是天也。众人则有天有人。又至有过不及矣。程子之对天理言人心。自非三言之本意耳。
第三十八板○答张敬夫书。盖舜禹受授之际。所以谓人心私欲者。非若众人所谓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则虽云本是道心之发。然终未离人心之境。所谓动以人则有妄。颜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间者是也。既曰有妄。则非私欲而何。
必有事焉而勿正人也。鸢飞鱼跃天也。然程子以为意思同。今有一毫把捉底意思者以为人则可也。以为妄以为私欲。则分数太过。盖以程子对天理之人心。合大舜对道心之人心言故如此。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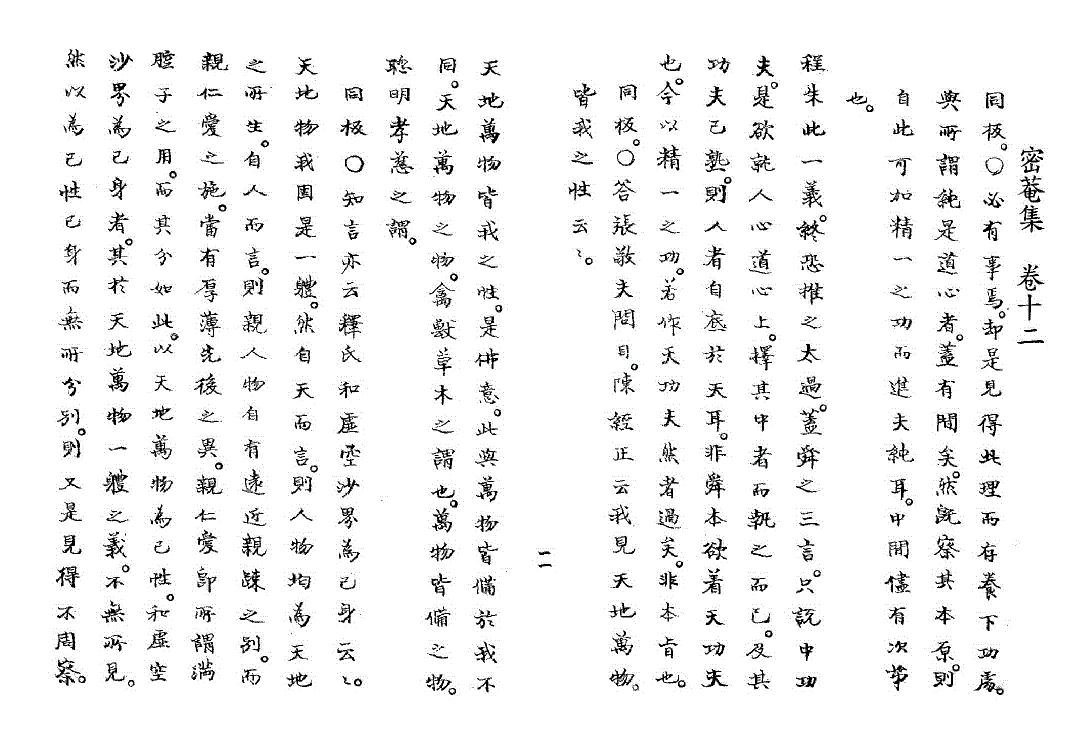 同板○必有事焉。却是见得此理而存养下功处。与所谓纯是道心者。盖有间矣。然既察其本原。则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进夫纯耳。中间尽有次第也。
同板○必有事焉。却是见得此理而存养下功处。与所谓纯是道心者。盖有间矣。然既察其本原。则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进夫纯耳。中间尽有次第也。程朱此一义。终恐推之太过。盖舜之三言。只说中功夫。是欲就人心道心上。择其中者而执之而已。及其功夫已熟。则人者自底于天耳。非舜本欲着天功夫也。今以精一之功。若作天功夫然者过矣。非本旨也。
同板○答张敬夫问目。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云云。
天地万物皆我之性。是佛意。此与万物皆备于我不同。天地万物之物。禽兽草木之谓也。万物皆备之物。聪明孝慈之谓。
同板○知言亦云释氏和虚空沙界为己身云云。
天地物我固是一体。然自天而言。则人物均为天地之所生。自人而言。则亲人物自有远近亲疏之别。而亲仁爱之施。当有厚薄先后之异。亲仁爱即所谓满腔子之用。而其分如此。以天地万物为己性。和虚空沙界为己身者。其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义。不无所见。然以为己性己身而无所分别。则又是见得不周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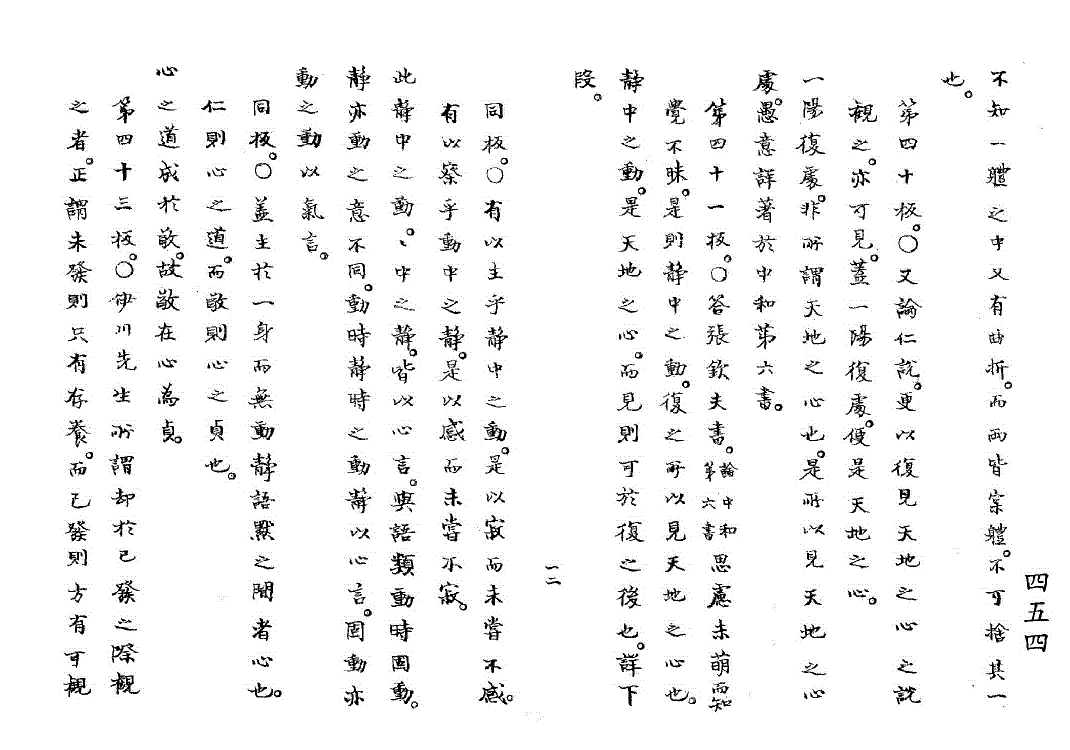 不知一体之中又有曲折。而两皆宲体。不可舍其一也。
不知一体之中又有曲折。而两皆宲体。不可舍其一也。第四十板○又论仁说。更以复见天地之心之说观之。亦可见。盖一阳复处。便是天地之心。
一阳复处。非所谓天地之心也。是所以见天地之心处。愚意详著于中和第六书。
第四十一板○答张钦夫书。(论中和第六书)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
静中之动。是天地之心。而见则可于复之后也。详下段。
同板○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以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以感而未尝不寂。
此静中之动。动中之静。皆以心言。与语类动时固动。静亦动之意不同。动时静时之动静以心言。固动亦动之动以气言。
同板○盖主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
心之道成于敬。故敬在心为贞。
第四十三板○伊川先生所谓却于已发之际观之者。正谓未发则只有存养。而已发则方有可观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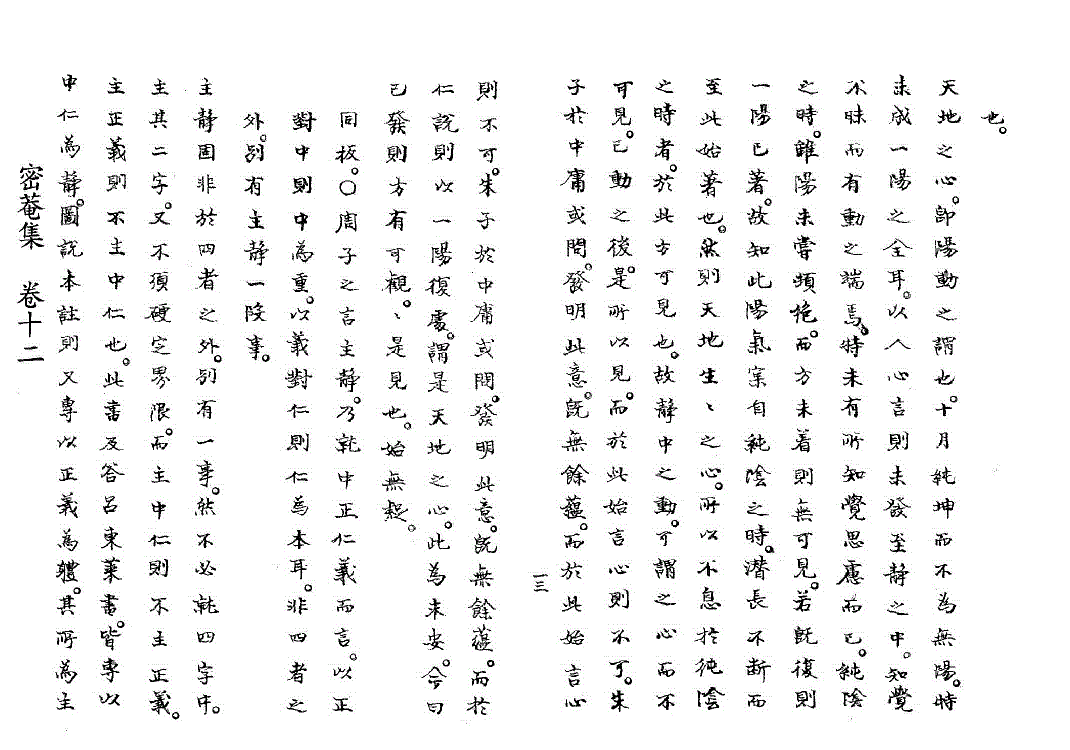 也。
也。天地之心。即阳动之谓也。十月纯坤而不为无阳。特未成一阳之全耳。以人心言则未发至静之中。知觉不昧而有动之端焉。特未有所知觉思虑而已。纯阴之时。虽阳未尝顿绝。而方未着则无可见。若既复则一阳已著。故知此阳气宲自纯阴之时。潜长不断而至此始著也。然则天地生生之心。所以不息于纯阴之时者。于此方可见也。故静中之动。可谓之心而不可见。已动之后。是所以见。而于此始言心则不可。朱子于中庸或问。发明此意。既无馀蕴。而于此始言心则不可。朱子于中庸或问。发明此意。既无馀蕴。而于仁说则以一阳复处。谓是天地之心。此为未安。今曰已发则方有可观。观是见也。始无疑。
同板○周子之言主静。乃就中正仁义而言。以正对中则中为重。以义对仁则仁为本耳。非四者之外。别有主静一段事。
主静固非于四者之外。别有一事。然不必就四字中。主其二字。又不须硬定界限。而主中仁则不主正义。主正义则不主中仁也。此书及答吕东莱书。皆专以中仁为静。图说本注则又专以正义为体。其所为主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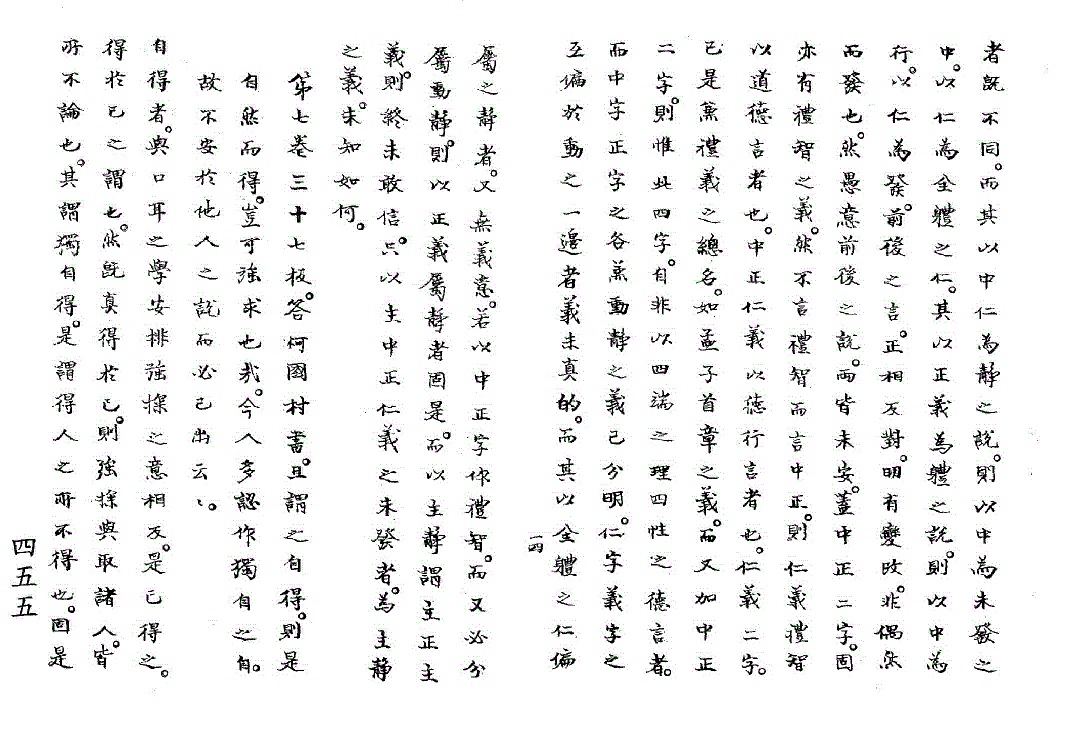 者既不同。而其以中仁为静之说。则以中为未发之中。以仁为全体之仁。其以正义为体之说。则以中为行。以仁为发。前后之言。正相反对。明有变改。非偶然而发也。然愚意前后之说。两皆未安。盖中正二字。固亦有礼智之义。然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则仁义礼智以道德言者也。中正仁义以德行言者也。仁义二字。已是兼礼义之总名。如孟子首章之义。而又加中正二字。则惟此四字。自非以四端之理四性之德言者。而中字正字之各兼动静之义已分明。仁字义字之互偏于动之一边者义未真的。而其以全体之仁偏属之静者。又无义意。若以中正字作礼智。而又必分属动静。则以正义属静者固是。而以主静谓主正主义。则终未敢信。只以主中正仁义之未发者。为主静之义。未知如何。
者既不同。而其以中仁为静之说。则以中为未发之中。以仁为全体之仁。其以正义为体之说。则以中为行。以仁为发。前后之言。正相反对。明有变改。非偶然而发也。然愚意前后之说。两皆未安。盖中正二字。固亦有礼智之义。然不言礼智而言中正。则仁义礼智以道德言者也。中正仁义以德行言者也。仁义二字。已是兼礼义之总名。如孟子首章之义。而又加中正二字。则惟此四字。自非以四端之理四性之德言者。而中字正字之各兼动静之义已分明。仁字义字之互偏于动之一边者义未真的。而其以全体之仁偏属之静者。又无义意。若以中正字作礼智。而又必分属动静。则以正义属静者固是。而以主静谓主正主义。则终未敢信。只以主中正仁义之未发者。为主静之义。未知如何。第七卷三十七板○答柯国材书。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己出云云。
自得者。与口耳之学安排强探之意相反。是己得之。得于己之谓也。然既真得于己。则强探与取诸人。皆所不论也。其谓独自得。是谓得人之所不得也。固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6H 页
 自私狭小。非君子之所用心也。然若只作自然之义。则亦似不周匝。盖自然之意。未能该得于己之义也。孟子集注作自然得于己。此为差稳。然以自作自然之意。则于己字无交涉。而以自作己之义。则己得之之时。其不靠人不强探之意。自包入矣。况真得于己则至矣。又其靠人强探。皆非所论也。可知己字之义为重。而自然字非正义也。
自私狭小。非君子之所用心也。然若只作自然之义。则亦似不周匝。盖自然之意。未能该得于己之义也。孟子集注作自然得于己。此为差稳。然以自作自然之意。则于己字无交涉。而以自作己之义。则己得之之时。其不靠人不强探之意。自包入矣。况真得于己则至矣。又其靠人强探。皆非所论也。可知己字之义为重。而自然字非正义也。第四十五板○答许顺之书。心一也。操而存则义理明而谓之道心。舍而亡则物欲肆而谓之人心云云。
以存为道心。以亡为人心。此说与舜所说人心道心危微之义不同。盖初说也。又有定论。
第四十九板○答王近思书。此是本心陷溺之久。义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读书穷理。常不间断。则物欲之心。自不能胜。而本心义理安且固矣。
既曰平时不惑于是非者。犹复如此。则此非专不为穷理之病也。是不能存养本心。己有未克而然也。但以穷理为言。恐未切实。恐亦初年法门。
第八卷十九板○答何叔京书。盖此心操之则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于觉而操之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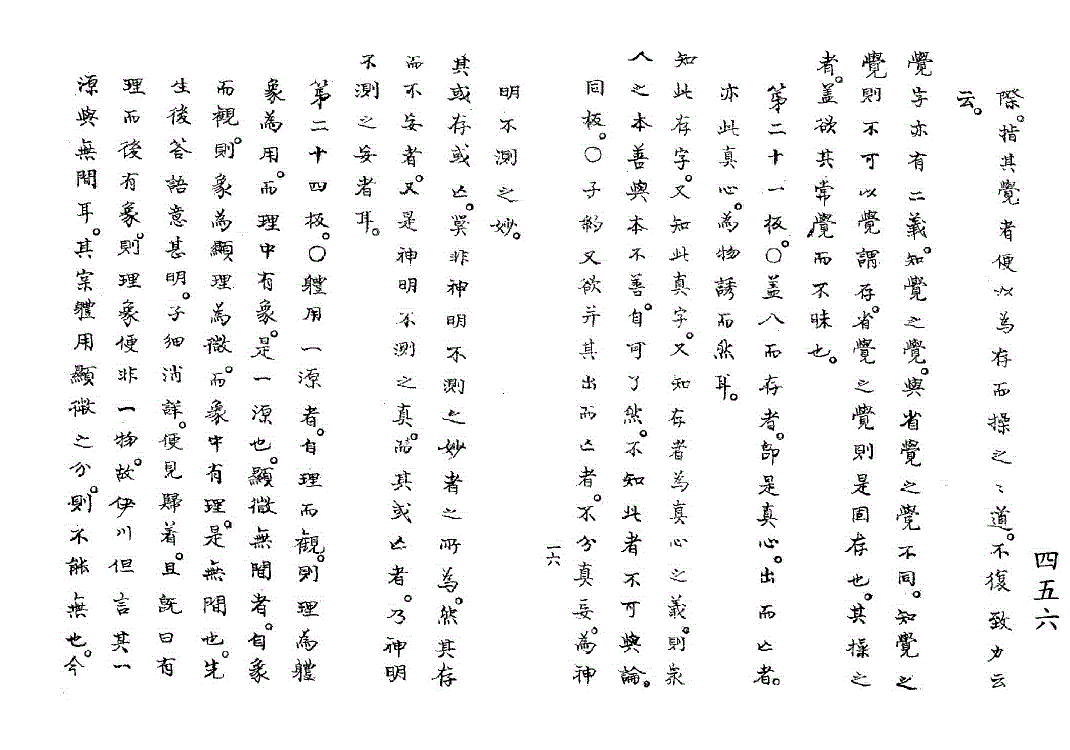 际。指其觉者便以为存而操之之道。不复致力云云。
际。指其觉者便以为存而操之之道。不复致力云云。觉字亦有二义。知觉之觉。与省觉之觉不同。知觉之觉则不可以觉谓存。省觉之觉则是固存也。其操之者。盖欲其常觉而不昧也。
第二十一板○盖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为物诱而然耳。
知此存字。又知此真字。又知存者为真心之义。则众人之本善与本不善。自可了然。不知此者不可与论。
同板○子约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妄。为神明不测之妙。
其或存或亡。莫非神明不测之妙者之所为。然其存而不妄者。又是神明不测之真。而其或亡者。乃神明不测之妄者耳。
第二十四板○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先生后答语意甚明。子细消详。便见归着。且既曰有理而后有象。则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与无间耳。其宲体用显微之分。则不能无也。今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7H 页
 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别。恐陷于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别。恐陷于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朱子此书。其于分别体分之义。岂不晓然。盖既理为体象为用。则体者一源也。用者分殊也。一原者万物所同然也。分殊者万物所以异也。前书以仁义礼智为天理之件数。而件数者。即以象而有件有数矣。此所以论天理论其体。则一而无二。论气象论其分。则众象不一矣。以此等观之。则知朱子之以仁义礼智为性之全体者。其意未始为物物皆全此四德之全也。偏全错综。其分不一。而不出于五常之外也。若其言性同之义。则又不以全此四者之全为言也。但其为天理为体者一而已也。今以论人心未发之理本全四者之全之义。移作一原之体物物皆全四者之全之义者。虽有朱子之说近似者。其意则以此推之。而可知其必不然耳。盖天理不是硬定之物事。只是自然而真实之道理而已。统而言之。万象皆是理矣。岂是象象各兼万象者乎。若非象象各兼万象者。则象(一字缺)一象之物。又安得各兼万象乎。理象便非一物。体用之分。不能无矣。象则万象森然之象。而自未应已是象矣。故若谓此理之体为万象之体。而为万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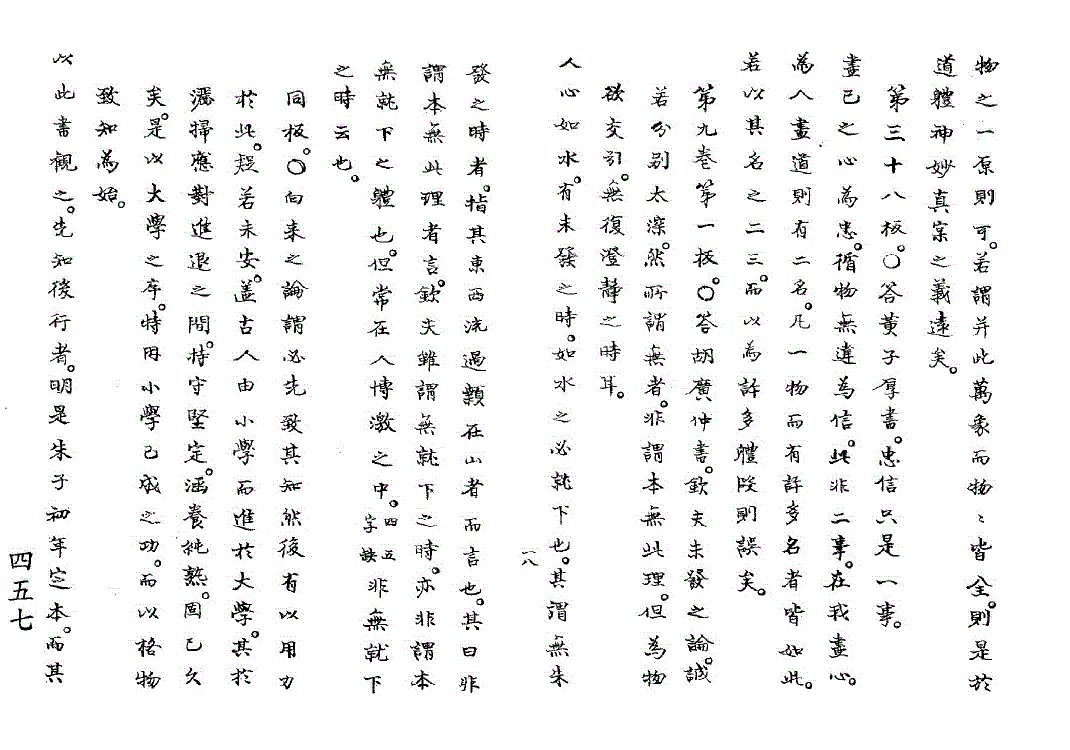 物之一原则可。若谓并此万象而物物皆全。则是于道体神妙真宲之义远矣。
物之一原则可。若谓并此万象而物物皆全。则是于道体神妙真宲之义远矣。第三十八板○答黄子厚书。忠信只是一事。
尽己之心为忠。循物无违为信。此非二事。在我尽心。为人尽道则有二名。凡一物而有许多名者皆如此。若以其名之二三。而以为许多体段则误矣。
第九卷第一板○答胡广仲书。钦夫未发之论。诚若分别太深。然所谓无者。非谓本无此理。但为物欲交引。无复澄静之时耳。
人心如水。有未发之时。如水之必就下也。其谓无朱(一作未)发之时者。指其东西流过颡在山者而言也。其曰非谓本无此理者言。钦夫虽谓无就下之时。亦非谓本无就下之体也。但常在人博激之中。(四五字缺)非无就下之时云也。
同板○向来之论谓必先致其知然后有以用力于此。疑若未安。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
以此书观之。先知后行者。明是朱子初年定本。而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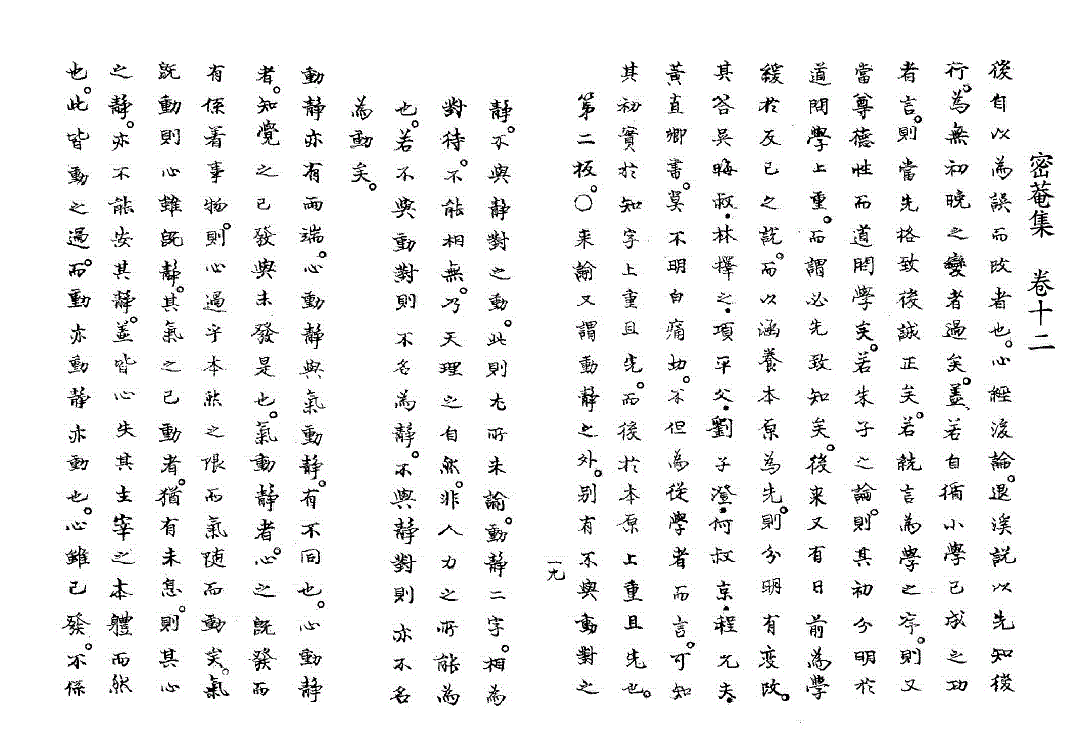 后自以为误而改者也。心经后论。退溪说以先知后行。为无初晚之变者过矣。盖若自循小学已成之功者言。则当先格致后诚正矣。若统言为学之序。则又当尊德性而道问学矣。若朱子之论。则其初分明于道问学上重。而谓必先致知矣。后来又有日前为学缓于反己之说。而以涵养本原为先。则分明有变改。其答吴晦叔,林择之,项平父,刘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黄直卿书。莫不明白痛切。不但为从学者而言。可知其初实于知字上重且先。而后于本原上重且先也。
后自以为误而改者也。心经后论。退溪说以先知后行。为无初晚之变者过矣。盖若自循小学已成之功者言。则当先格致后诚正矣。若统言为学之序。则又当尊德性而道问学矣。若朱子之论。则其初分明于道问学上重。而谓必先致知矣。后来又有日前为学缓于反己之说。而以涵养本原为先。则分明有变改。其答吴晦叔,林择之,项平父,刘子澄,何叔京,程允夫,黄直卿书。莫不明白痛切。不但为从学者而言。可知其初实于知字上重且先。而后于本原上重且先也。第二板○来谕又谓动静之外。别有不与动对之静。不与静对之动。此则尤所未谕。动静二字。相为对待。不能相无。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若不与动对则不名为静。不与静对则亦不名为动矣。
动静亦有两端。心动静与气动静。有不同也。心动静者。知觉之已发与未发是也。气动静者。心之既发而有系着事物。则心过乎本然之限而气随而动矣。气既动则心虽既静。其气之已动者。犹有未息。则其心之静。亦不能安其静。盖皆心失其主宰之本体而然也。此皆动之过。而动亦动静亦动也。心虽已发。不系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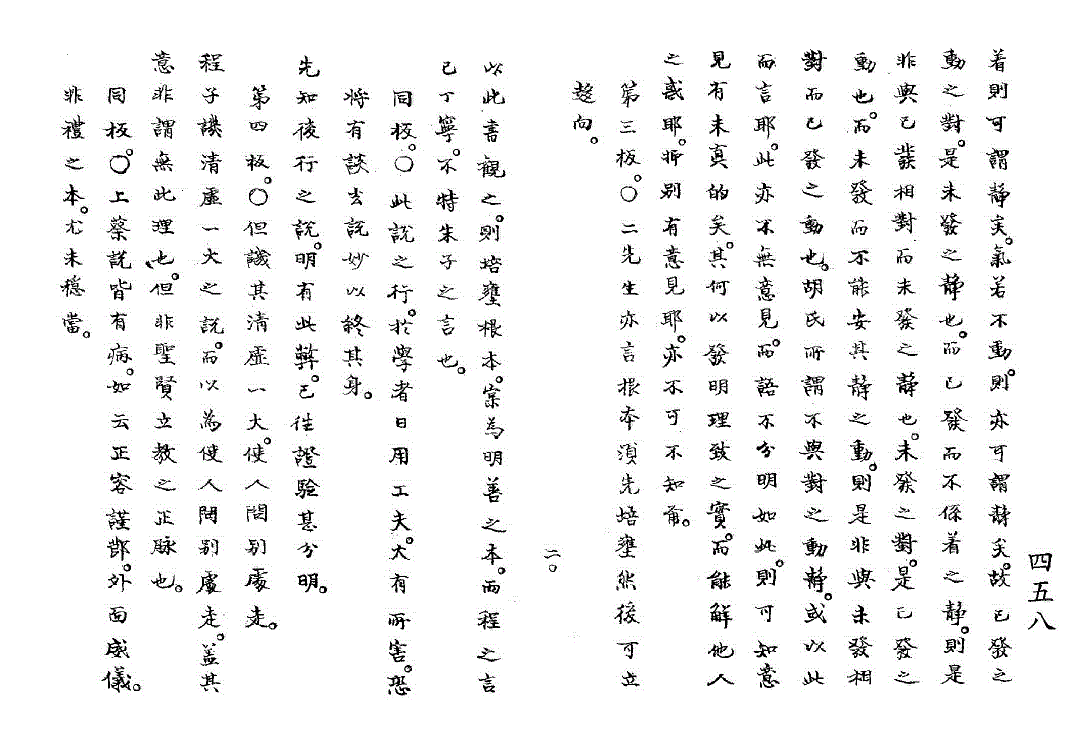 着则可谓静矣。气若不动。则亦可谓静矣。故已发之动之对。是未发之静也。而已发而不系着之静。则是非与已发相对而未发之静也。未发之对。是已发之动也。而未发而不能安其静之动。则是非与未发相对而已发之动也。胡氏所谓不与对之动静。或以此而言耶。此亦不无意见。而语不分明如此。则可知意见有未真的矣。其何以发明理致之实。而能解他人之惑耶。抑别有意见耶。亦不可不知尔。
着则可谓静矣。气若不动。则亦可谓静矣。故已发之动之对。是未发之静也。而已发而不系着之静。则是非与已发相对而未发之静也。未发之对。是已发之动也。而未发而不能安其静之动。则是非与未发相对而已发之动也。胡氏所谓不与对之动静。或以此而言耶。此亦不无意见。而语不分明如此。则可知意见有未真的矣。其何以发明理致之实。而能解他人之惑耶。抑别有意见耶。亦不可不知尔。第三板○二先生亦言根本须先培壅然后可立趍向。
以此书观之。则培壅根本。宲为明善之本。两程之言已丁宁。不特朱子之言也。
同板○此说之行。于学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将有谈玄说妙以终其身。
先知后行之说。明有此弊。已往證验甚分明。
第四板○但讥其清虚一大。使人问别处走。
程子讥清虚一大之说。而以为使人问别处走。盖其意非谓无此理也。但非圣贤立教之正脉也。
同板○上蔡说皆有病。如云正容谨节。外面威仪。非礼之本。尤未稳当。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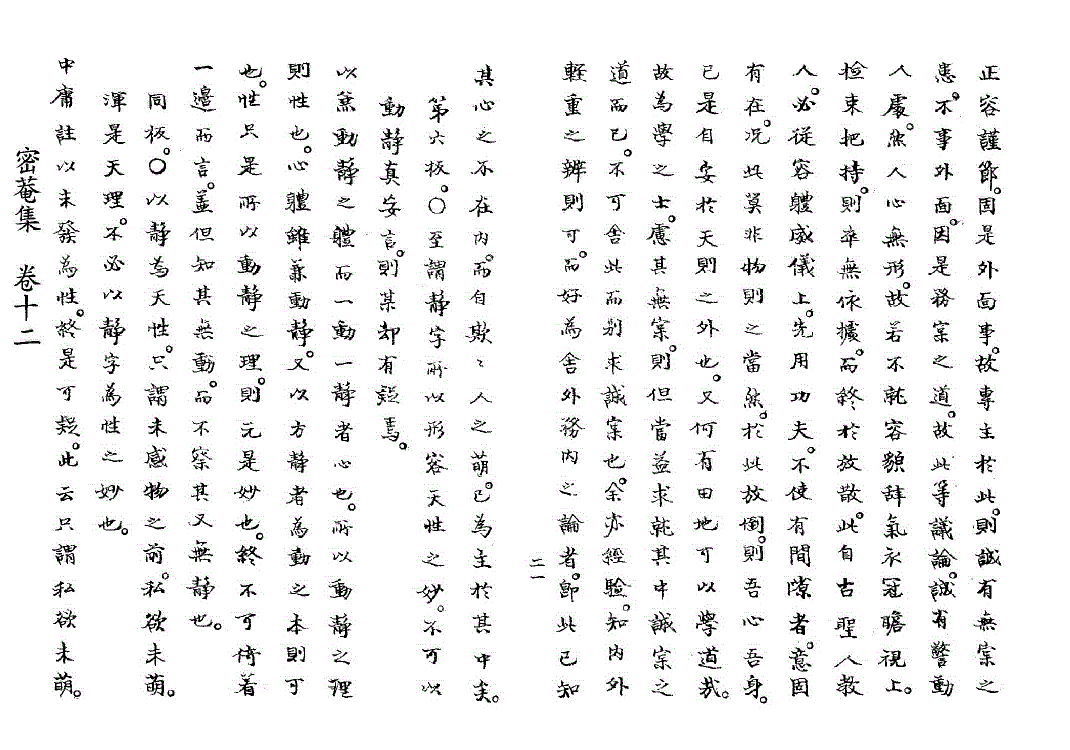 正容谨节。固是外面事。故专主于此。则诚有无宲之患。不事外面。因是务宲之道。故此等议论。诚有警动人处。然人心无形。故若不就容貌辞气衣冠瞻视上。检束把持。则卒无依据。而终于放散。此自古圣人教人。必从容体威仪上。先用功夫。不使有间隙者。意固有在。况此莫非物则之当然。于此放倒。则吾心吾身。已是自安于天则之外也。又何有田地可以学道哉。故为学之士。虑其无宲。则但当益求就其中诚宲之道而已。不可舍此而别求诚宲也。余亦经验。知内外轻重之辨则可。而好为舍外务内之论者。即此已知其心之不在内。而自欺欺人之萌。已为主于其中矣。
正容谨节。固是外面事。故专主于此。则诚有无宲之患。不事外面。因是务宲之道。故此等议论。诚有警动人处。然人心无形。故若不就容貌辞气衣冠瞻视上。检束把持。则卒无依据。而终于放散。此自古圣人教人。必从容体威仪上。先用功夫。不使有间隙者。意固有在。况此莫非物则之当然。于此放倒。则吾心吾身。已是自安于天则之外也。又何有田地可以学道哉。故为学之士。虑其无宲。则但当益求就其中诚宲之道而已。不可舍此而别求诚宲也。余亦经验。知内外轻重之辨则可。而好为舍外务内之论者。即此已知其心之不在内。而自欺欺人之萌。已为主于其中矣。第六板○至谓静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动静真妄言。则某却有疑焉。
以兼动静之体而一动一静者心也。所以动静之理则性也。心体虽兼动静。又以方静者为动之本则可也。性只是所以动静之理。则元是妙也。终不可倚着一边而言。盖但知其无动。而不察其又无静也。
同板○以静为天性。只谓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浑是天理。不必以静字为性之妙也。
中庸注以未发为性。终是可疑。此云只谓私欲未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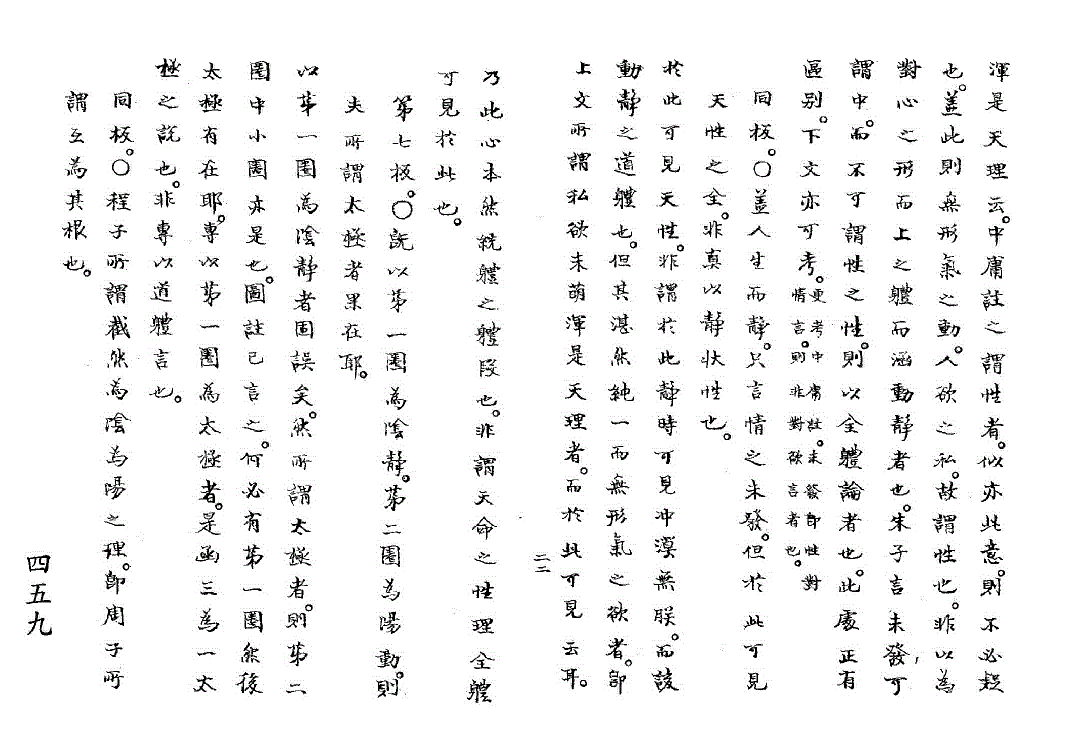 浑是天理云。中庸注之谓性者。似亦此意。则不必疑也。盖此则无形气之动。人欲之私。故谓性也。非以为对心之形而上之体而涵动静者也。朱子言未发可谓中。而不可谓性之性。则以全体论者也。此处正有区别。下文亦可考。(更考中庸注。未发即性对情言。则非对欲言者也。)
浑是天理云。中庸注之谓性者。似亦此意。则不必疑也。盖此则无形气之动。人欲之私。故谓性也。非以为对心之形而上之体而涵动静者也。朱子言未发可谓中。而不可谓性之性。则以全体论者也。此处正有区别。下文亦可考。(更考中庸注。未发即性对情言。则非对欲言者也。)同板○盖人生而静。只言情之未发。但于此可见天性之全。非真以静状性也。
于此可见天性。非谓于此静时可见冲漠无朕。而该动静之道体也。但其湛然纯一而无形气之欲者。即上文所谓私欲未萌浑是天理者。而于此可见云耳。乃此心本然统体之体段也。非谓天命之性理全体可见于此也。
第七板○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在耶。
以第一圈为阴静者固误矣。然所谓太极者。则第二圈中小圈亦是也。图注已言之。何必有第一圈然后太极有在耶。专以第一圈为太极者。是函三为一太极之说也。非专以道体言也。
同板○程子所谓截然为阴为阳之理。即周子所谓互为其根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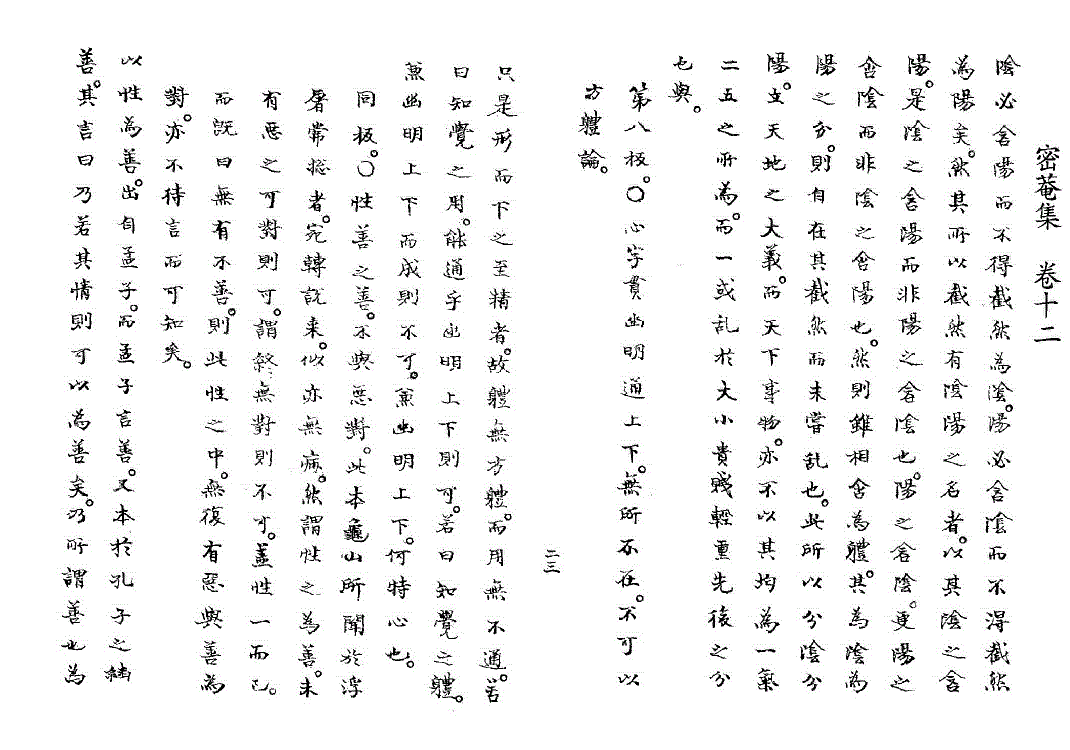 阴必含阳而不得截然为阴。阳必含阴而不得截然为阳矣。然其所以截然有阴阳之名者。以其阴之含阳。是阴之含阳而非阳之含阴也。阳之含阴。更阳之含阴而非阴之含阳也。然则虽相含为体。其为阴为阳之分。则自在其截然而未尝乱也。此所以分阴分阳。立天地之大义。而天下事物。亦不以其均为一气二五之所为。而一或乱于大小贵贱轻重先后之分也与。
阴必含阳而不得截然为阴。阳必含阴而不得截然为阳矣。然其所以截然有阴阳之名者。以其阴之含阳。是阴之含阳而非阳之含阴也。阳之含阴。更阳之含阴而非阴之含阳也。然则虽相含为体。其为阴为阳之分。则自在其截然而未尝乱也。此所以分阴分阳。立天地之大义。而天下事物。亦不以其均为一气二五之所为。而一或乱于大小贵贱轻重先后之分也与。第八板○心字贯幽明通上下。无所不在。不可以方体论。
只是形而下之至精者。故体无方体。而用无不通。若曰知觉之用。能通乎幽明上下则可。若曰知觉之体。兼幽明上下而成则不可。兼幽明上下。何特心也。
同板○性善之善。不与恶对。此本龟山所闻于浮屠常总者。宛转说来。似亦无病。然谓性之为善。未有恶之可对则可。谓终无对则不可。盖性一而已。而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以性为善。出自孟子。而孟子言善。又本于孔子之继善。其言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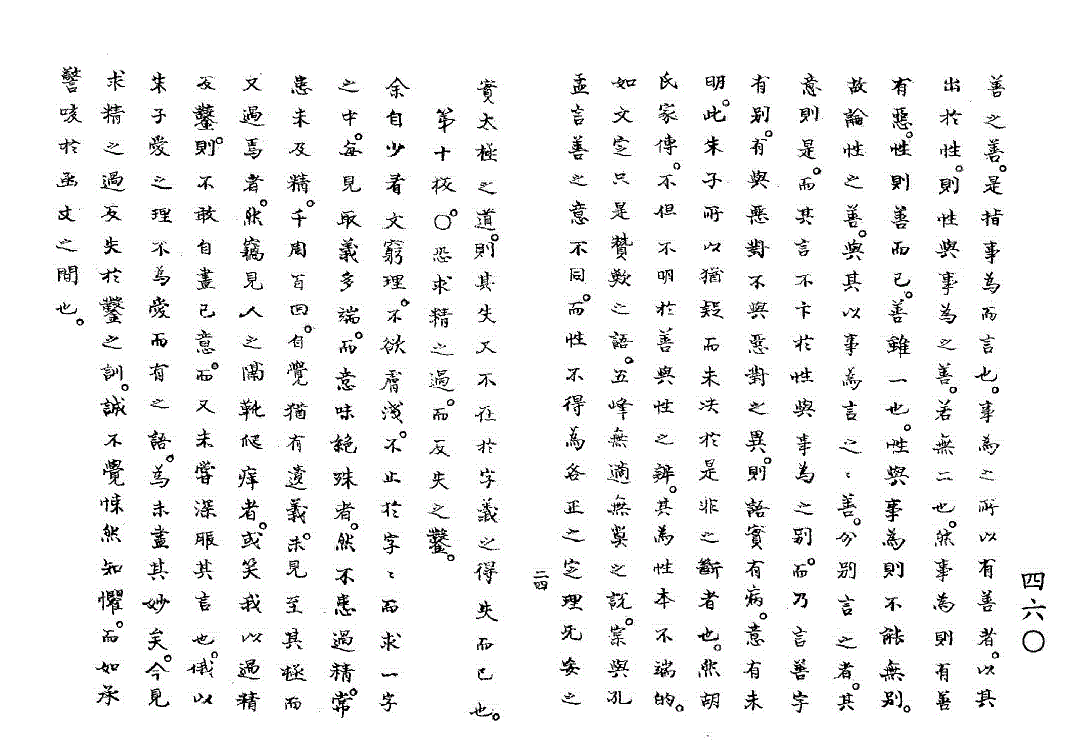 善之善。是指事为而言也。事为之所以有善者。以其出于性。则性与事为之善。若无二也。然事为则有善有恶。性则善而已。善虽一也。性与事为则不能无别。故论性之善。与其以事为言之之善。分别言之者。其意则是。而其言不卞于性与事为之别。而乃言善字有别。有与恶对不与恶对之异。则语实有病。意有未明。此朱子所以犹疑而未决于是非之断者也。然胡氏家传。不但不明于善与性之辨。其为性本不端的。如文定只是赞叹之语。五峰无适无莫之说。宲与孔孟言善之意不同。而性不得为各正之定理无妄之实太极之道。则其失又不在于字义之得失而已也。
善之善。是指事为而言也。事为之所以有善者。以其出于性。则性与事为之善。若无二也。然事为则有善有恶。性则善而已。善虽一也。性与事为则不能无别。故论性之善。与其以事为言之之善。分别言之者。其意则是。而其言不卞于性与事为之别。而乃言善字有别。有与恶对不与恶对之异。则语实有病。意有未明。此朱子所以犹疑而未决于是非之断者也。然胡氏家传。不但不明于善与性之辨。其为性本不端的。如文定只是赞叹之语。五峰无适无莫之说。宲与孔孟言善之意不同。而性不得为各正之定理无妄之实太极之道。则其失又不在于字义之得失而已也。第十板○恐求精之过。而反失之凿。
余自少看文穷理。不欲肤浅。不止于字字而求一字之中。每见取义多端。而意味绝殊者。然不患过精。常患未及精。千周百回。自觉犹有遗义。未见至其极而又过焉者。然窃见人之隔靴爬痒者。或笑我以过精反凿。则不敢自尽己意。而又未尝深服其言也。俄以朱子爱之理不为爱而有之语。为未尽其妙矣。今见求精之过反失于凿之训。诚不觉悚然知惧。而如承譬咳于函丈之间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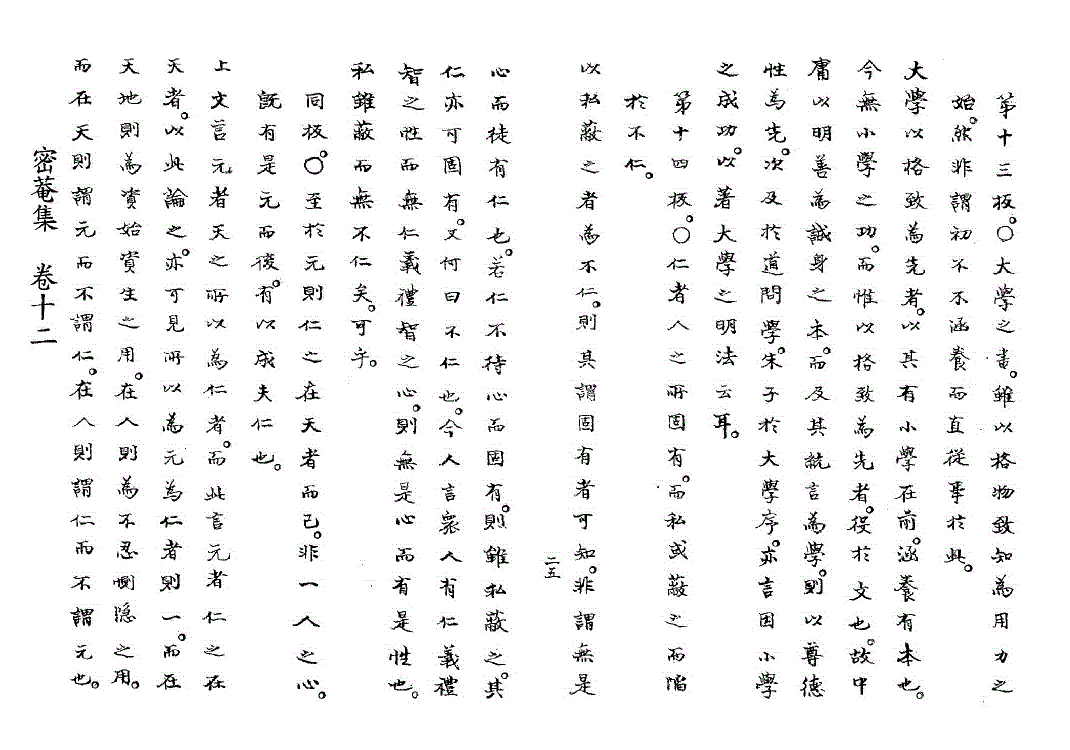 第十三板○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不涵养而直从事于此。
第十三板○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不涵养而直从事于此。大学以格致为先者。以其有小学在前。涵养有本也。今无小学之功。而惟以格致为先者。役于文也。故中庸以明善为诚身之本。而及其统言为学。则以尊德性为先。次及于道问学。朱子于大学序。亦言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云耳。
第十四板○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而陷于不仁。
以私蔽之者为不仁。则其谓固有者可知。非谓无是心而徒有仁也。若仁不待心而固有。则虽私蔽之。其仁亦可固有。又何曰不仁也。今人言众人有仁义礼智之性而无仁义礼智之心。则无是心而有是性也。私虽蔽而无不仁矣。可乎。
同板○至于元则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
上文言元者天之所以为仁者。而此言元者仁之在天者。以此论之。亦可见所以为元为仁者则一。而在天地则为资始资生之用。在人则为不忍恻隐之用。而在天则谓元而不谓仁。在人则谓仁而不谓元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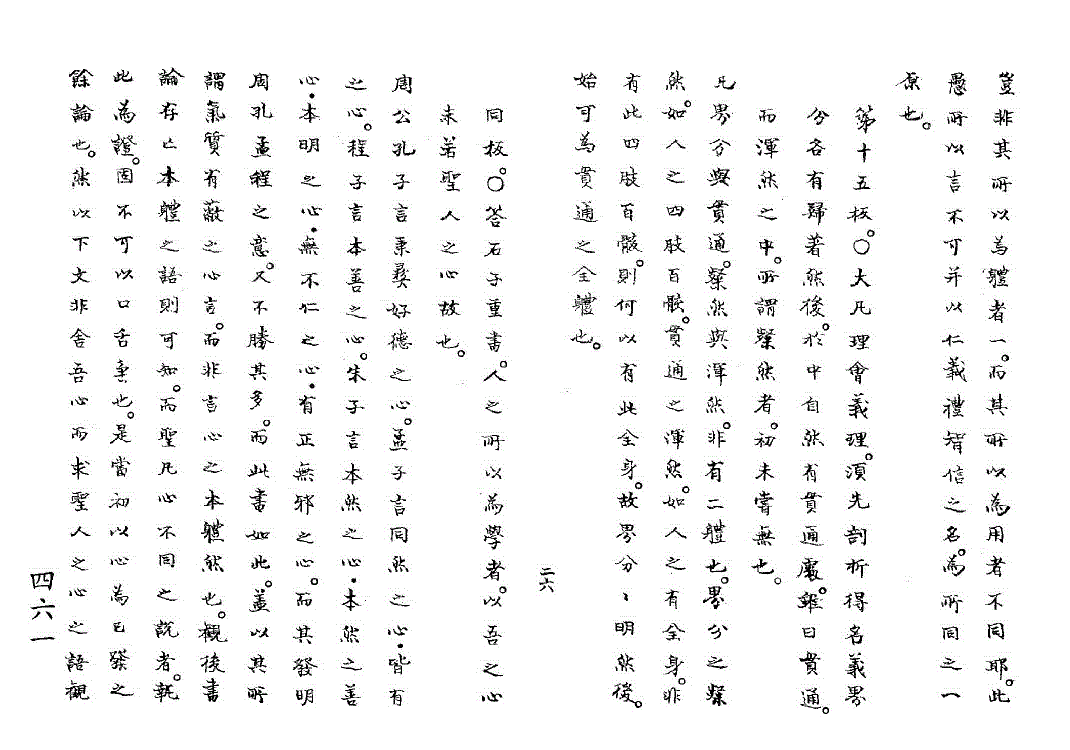 岂非其所以为体者一。而其所以为用者不同耶。此愚所以言不可并以仁义礼智信之名。为所同之一原也。
岂非其所以为体者一。而其所以为用者不同耶。此愚所以言不可并以仁义礼智信之名。为所同之一原也。第十五板○大凡理会义理。须先剖析得名义界分各有归著然后。于中自然有贯通处。虽曰贯通。而浑然之中。所谓粲然者。初未尝无也。
凡界分与贯通。粲然与浑然。非有二体也。界分之粲然。如人之四肢百骸。贯通之浑然。如人之有全身。非有此四肢百骸。则何以有此全身。故界分分明然后。始可为贯通之全体也。
同板○答石子重书。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
周公孔子言秉彝好德之心。孟子言同然之心,皆有之心。程子言本善之心。朱子言本然之心,本然之善心,本明之心,无不仁之心,有正无邪之心。而其发明周孔孟程之意。又不胜其多。而此书如此。盖以其所谓气质有蔽之心言。而非言心之本体然也。观后书论存亡本体之语则可知。而圣凡心不同之说者。执此为證。固不可以口舌争也。是当初以心为已发之馀论也。然以下文非舍吾心而求圣人之心之语观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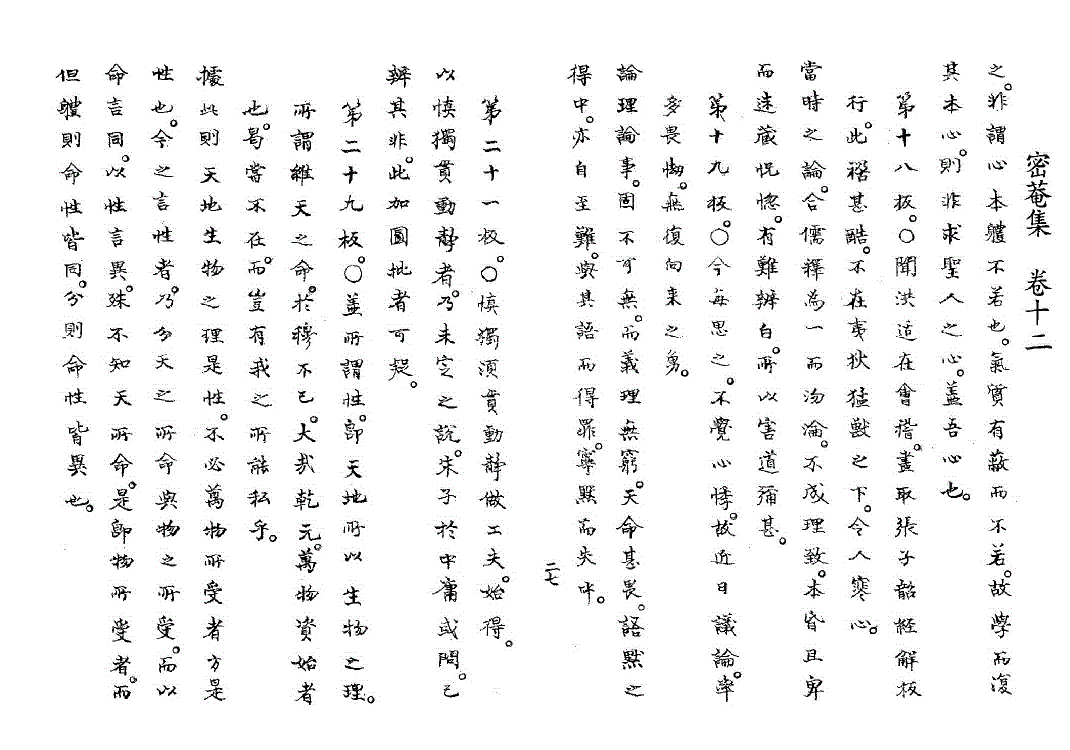 之。非谓心本体不若也。气质有蔽而不若。故学而复其本心。则非求圣人之心。盖吾心也。
之。非谓心本体不若也。气质有蔽而不若。故学而复其本心。则非求圣人之心。盖吾心也。第十八板○闻洪适在会稽。尽取张子韶经解板行。此𥚁甚酷。不在夷狄猛兽之下。令人寒心。
当时之论。合儒释为一而沕沦。不成理致。本昏且卑而迷藏恍惚。有难辨白。所以害道弥甚。
第十九板○今每思之。不觉心悸。故近日议论。率多畏㥘。无复向来之勇。
论理论事。固不可无。而义理无穷。天命甚畏。语默之得中。亦自至难。与其语而得罪。宁默而失中。
第二十一板○慎独须贯动静做工夫。始得。
以慎独贯动静者。乃未定之说。朱子于中庸或问。已辨其非。此加圆批者可疑。
第二十九板○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曷尝不在。而岂有我之所能私乎。
据此则天地生物之理是性。不必万物所受者方是性也。今之言性者。乃分天之所命与物之所受。而以命言同。以性言异。殊不知天所命。是即物所受者。而但体则命性皆同。分则命性皆异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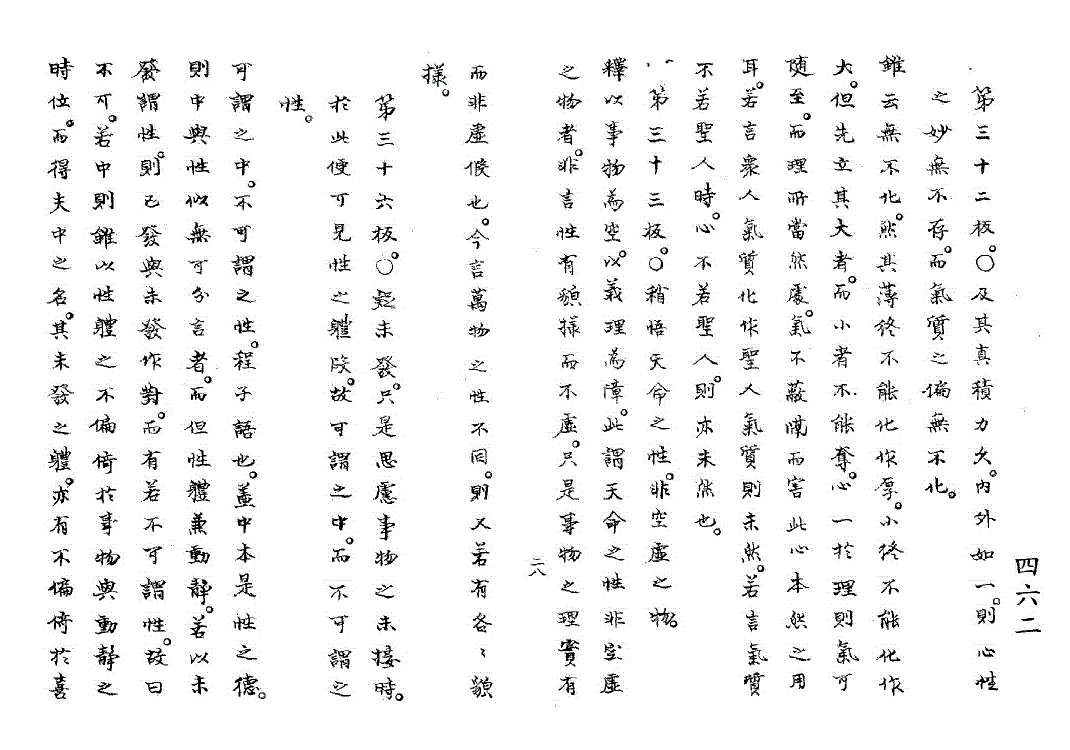 第三十二板○及其真积力久。内外如一。则心性之妙无不存。而气质之偏无不化。
第三十二板○及其真积力久。内外如一。则心性之妙无不存。而气质之偏无不化。虽云无不化。然其薄终不能化作厚。小终不能化作大。但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心一于理则气可随至。而理所当然处。气不蔽隔而害此心本然之用耳。若言众人气质化作圣人气质则未然。若言气质不若圣人时。心不若圣人。则亦未然也。
第三十三板○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虚之物。
释以事物为空。以义理为障。此谓天命之性非空虚之物者。非言性有貌㨾而不虚。只是事物之理实有而非虚假也。今言万物之性不同。则又若有各各貌㨾。
第三十六板○疑未发。只是思虑事物之未接时。于此便可见性之体段。故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
可谓之中。不可谓之性。程子语也。盖中本是性之德。则中与性似无可分言者。而但性体兼动静。若以未发谓性。则已发与未发作对。而有若不可谓性。故曰不可。若中则虽以性体之不偏倚于事物与动静之时位。而得夫中之名。其未发之体。亦有不偏倚于喜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3H 页
 怒哀乐。而可见性之体段。故可以通称也。
怒哀乐。而可见性之体段。故可以通称也。第三十八板○所论颜孟不同处。极言极善。正要见此曲折。始无窒碍耳。
圣人众人心本无异。但有存有不存。存之多存之少。此为不同。生来元存。故存之久而自明。明之至而自神。此圣人众人不同之大致。惟其存之不尽不固者。乃气浊之故。而明与不明系焉。此圣人论心。所以但以存亡为言。又言人皆有之,同然理义,秉彝好德。而卒无心异之说也。虽同圣。犹有钦思浚哲之别。此则资禀有异也。其心之体则如一也。众人亦有与圣人如一之体。而其资禀处。有拘蔽而害于本体之发用者。固多其品。然其所同之体则自如也。苟能存得自幼及长。则岂有不至。但既有拘蔽。故不能自存。而须费持守操存之功也。若无本体之同善。则又非徒用操存之功而可得。必有变心之功然后。乃可得乎本心之善也。今于此未透。而乃于心体上论浊驳。则众人元无本善之体。而存之一事。却无可施之地矣。以不存之心天飞渊沦之体。较之元存之心至明至神者。而谓人心元有许多不同。又以其飞沦之体为浊驳。则不省此其所谓亡者而非浊驳也。未之思耳。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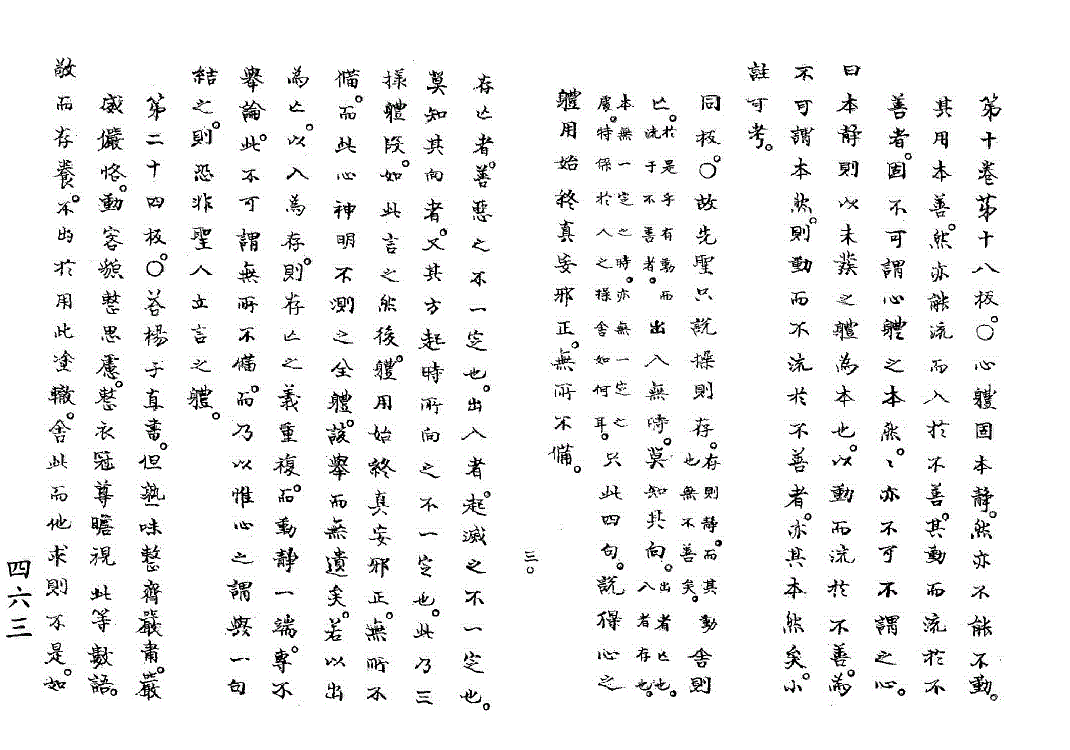 第十卷第十八板○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谓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
第十卷第十八板○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其用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其动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谓心体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谓之心。曰本静则以未发之体为本也。以动而流于不善。为不可谓本然。则动而不流于不善者。亦其本然矣。小注可考。
同板○故先圣只说操则存。(存则静。而其动也无不善矣。)舍则亡。(于是乎有动而流于不善者。)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无一定之时。亦无一定之处。特系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说得心之体用始终真妄邪正。无所不备。
存亡者。善恶之不一定也。出入者。起灭之不一定也。莫知其向者。又其方起时所向之不一定也。此乃三㨾体段。如此言之然后。体用始终真妄邪正。无所不备。而此心神明不测之全体。该举而无遗矣。若以出为亡。以入为存。则存亡之义重复。而动静一端。专不举论。此不可谓无所不备。而乃以惟心之谓与一句结之。则恐非圣人立言之体。
第二十四板○答杨子直书。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整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
敬而存养。不出于用此涂辙。舍此而他求则不是。如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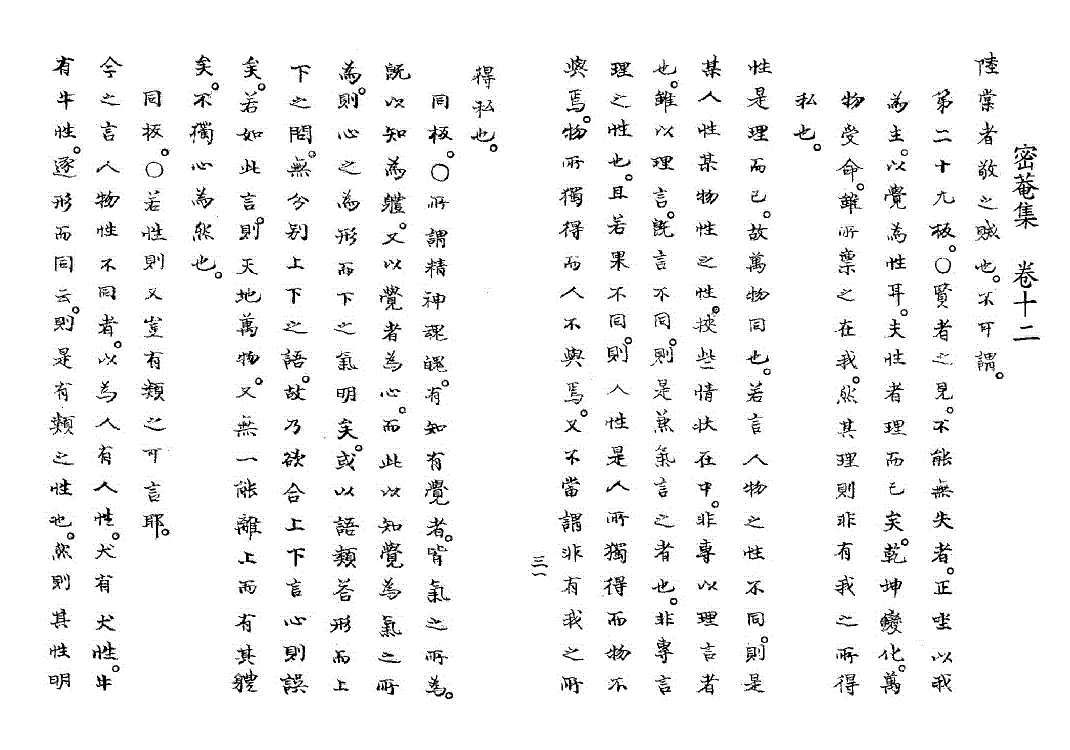 陆棠者敬之贼也。不可谓。
陆棠者敬之贼也。不可谓。第二十九板○贤者之见。不能无失者。正坐以我为主。以觉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性是理而已。故万物同也。若言人物之性不同。则是某人性某物性之性。挟些情状在中。非专以理言者也。虽以理言。既言不同。则是兼气言之者也。非专言理之性也。且若果不同。则人性是人所独得而物不与焉。物所独得而人不与焉。又不当谓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同板○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
既以知为体。又以觉者为心。而此以知觉为气之所为。则心之为形而下之气明矣。或以语类答形而上下之问。无分别上下之语。故乃欲合上下言心则误矣。若如此言。则天地万物。又无一能离上而有其体矣。不独心为然也。
同板○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耶。
今之言人物性不同者。以为人有人性。犬有犬性。牛有牛性。逐形而同云。则是有类之性也。然则其性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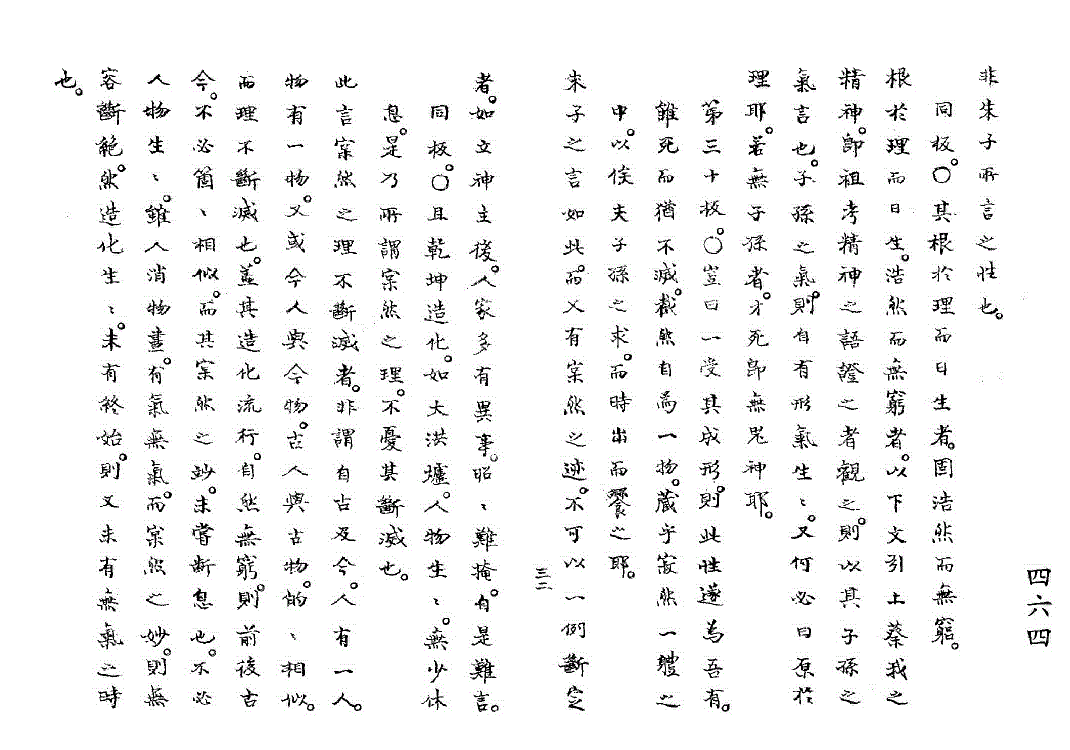 非朱子所言之性也。
非朱子所言之性也。同板○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无穷。
根于理而日生。浩然而无穷者。以下文引上蔡我之精神。即祖考精神之语證之者观之。则以其子孙之气言也。子孙之气。则自有形气生生。又何必曰原于理耶。若无子孙者。才死即无鬼神耶。
第三十板○岂曰一受其成形。则此性遂为吾有。虽死而犹不灭。截然自为一物。藏乎寂然一体之中。以俟夫子孙之求。而时出而飨之耶。
朱子之言如此。而又有宲然之迹。不可以一例断定者。如立神主后。人家多有异事。昭昭难掩。自是难言。
同板○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宲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
此言宲然之理不断灭者。非谓自古及今。人有一人。物有一物。又或今人与今物。古人与古物。的的相似。而理不断灭也。盖其造化流行。自然无穷。则前后古今。不必个个相似。而其宲然之妙。未尝断息也。不必人物生生。虽人消物尽。有气无气。而宲然之妙。则无容断绝。然造化生生。未有终始。则又未有无气之时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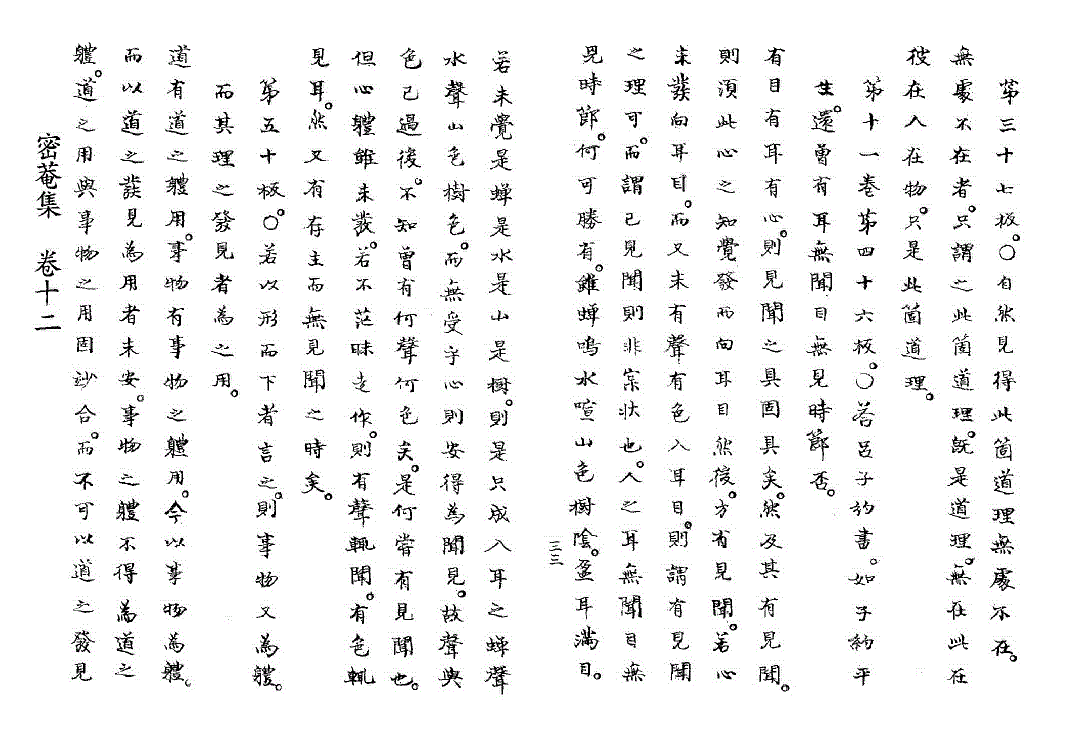 第三十七板○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
第三十七板○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无处不在者。只谓之此个道理。既是道理。无在此在彼在人在物。只是此个道理。
第十一卷第四十六板○答吕子约书。如子约平生。还曾有耳无闻目无见时节否。
有目有耳有心。则见闻之具固具矣。然及其有见闻。则须此心之知觉发而向耳目然后。方有见闻。若心未发向耳目。而又未有声有色入耳目。则谓有见闻之理可。而谓已见闻则非宲状也。人之耳无闻目无见时节。何可胜有。虽蝉鸣水喧山色树阴。盈耳满目。若未觉是蝉是水是山是树。则是只成入耳之蝉声水声山色树色。而无受乎心则安得为闻见。故声与色已过后。不知曾有何声何色矣。是何尝有见闻也。但心体虽未发。若不茫昧走作。则有声辄闻。有色辄见耳。然又有存主而无见闻之时矣。
第五十板○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
道有道之体用。事物有事物之体用。今以事物为体。而以道之发见为用者未安。事物之体不得为道之体。道之用与事物之用固妙合。而不可以道之发见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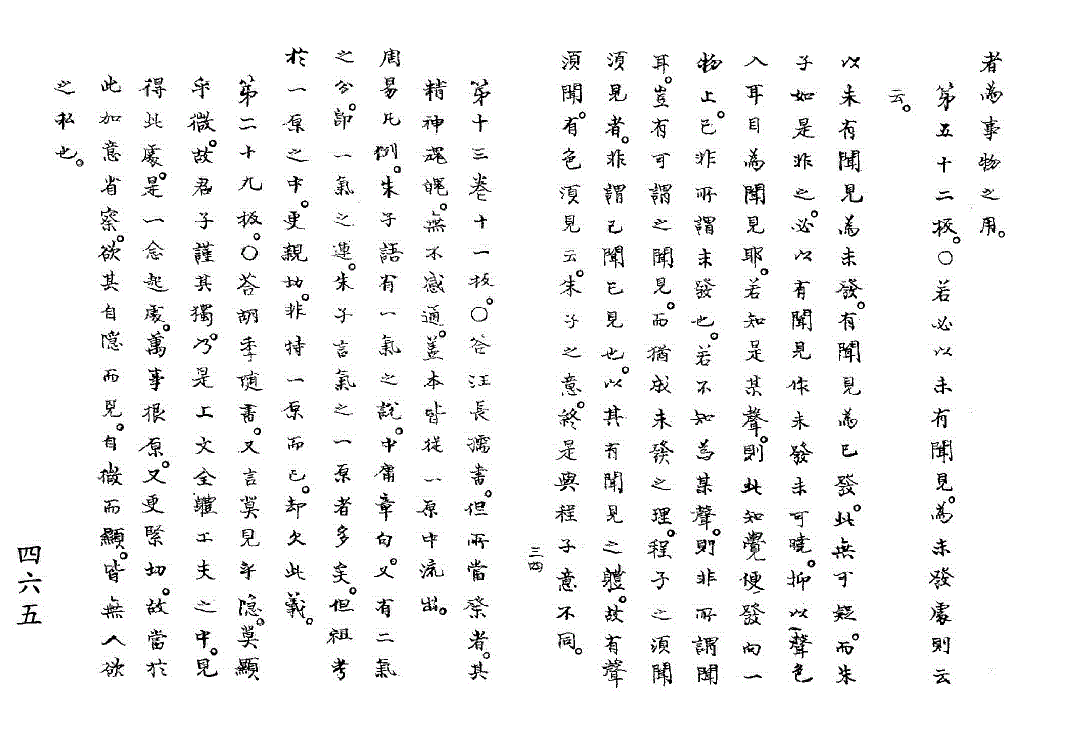 者为事物之用。
者为事物之用。第五十二板○若必以未有闻见。为未发处则云云。
以未有闻见为未发。有闻见为已发。此无可疑。而朱子如是非之。必以有闻见作未发未可晓。抑以声色入耳目为闻见耶。若知是某声。则此知觉便发向一物上。已非所谓未发也。若不知为某声。则非所谓闻耳。岂有可谓之闻见。而犹成未发之理。程子之须闻须见者。非谓已闻已见也。以其有闻见之体。故有声须闻。有色须见云。朱子之意。终是与程子意不同。
第十三卷十一板○答汪长孺书。但所当祭者。其精神魂魄。无不感通。盖本皆从一原中流出。
周易凡例。朱子语有一气之说。中庸章句。又有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朱子言气之一原者多矣。但祖考于一原之中。更亲切。非特一原而已。却欠此义。
第二十九板○答胡季随书。又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乃是上文全体工夫之中。见得此处。是一念起处。万事根原。又更紧切。故当于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隐而见。自微而显。皆无人欲之私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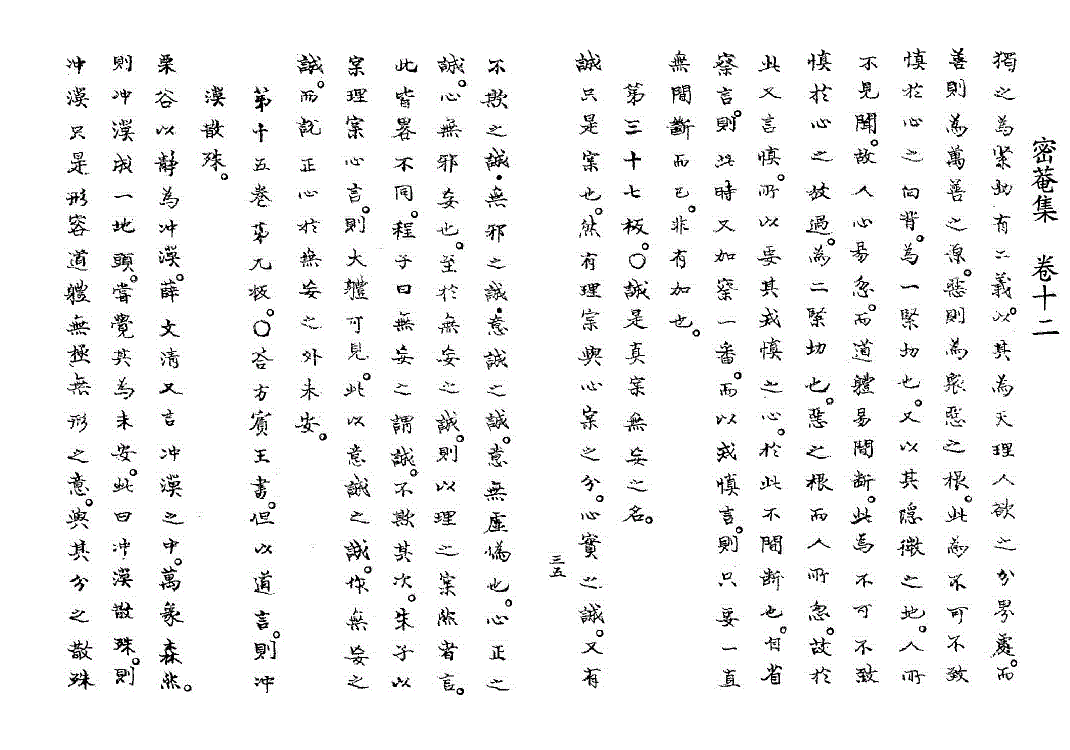 独之为紧切有二义。以其为天理人欲之分界处。而善则为万善之原。恶则为众恶之根。此为不可不致慎于心之向背。为一紧切也。又以其隐微之地。人所不见闻。故人心易忽。而道体易间断。此为不可不致慎于心之放过。为二紧切也。恶之根而人所忽。故于此又言慎。所以要其戒慎之心。于此不间断也。自省察言。则此时又加察一番。而以戒慎言。则只要一直无间断而已。非有加也。
独之为紧切有二义。以其为天理人欲之分界处。而善则为万善之原。恶则为众恶之根。此为不可不致慎于心之向背。为一紧切也。又以其隐微之地。人所不见闻。故人心易忽。而道体易间断。此为不可不致慎于心之放过。为二紧切也。恶之根而人所忽。故于此又言慎。所以要其戒慎之心。于此不间断也。自省察言。则此时又加察一番。而以戒慎言。则只要一直无间断而已。非有加也。第三十七板○诚是真宲无妄之名。
诚只是宲也。然有理宲与心宲之分。心实之诚。又有不欺之诚,无邪之诚,意诚之诚。意无虚伪也。心正之诚。心无邪妄也。至于无妄之诚。则以理之宲然者言。此皆略不同。程子曰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朱子以宲理宲心言。则大体可见。此以意诚之诚。作无妄之诚。而说正心于无妄之外未安。
第十五卷第九板○答方宾王书。但以道言。则冲漠散殊。
栗谷以静为冲漠。薛文清又言冲漠之中。万象森然。则冲漠成一地头。尝觉其为未安。此曰冲漠散殊。则冲漠只是形容道体无极无形之意。与其分之散殊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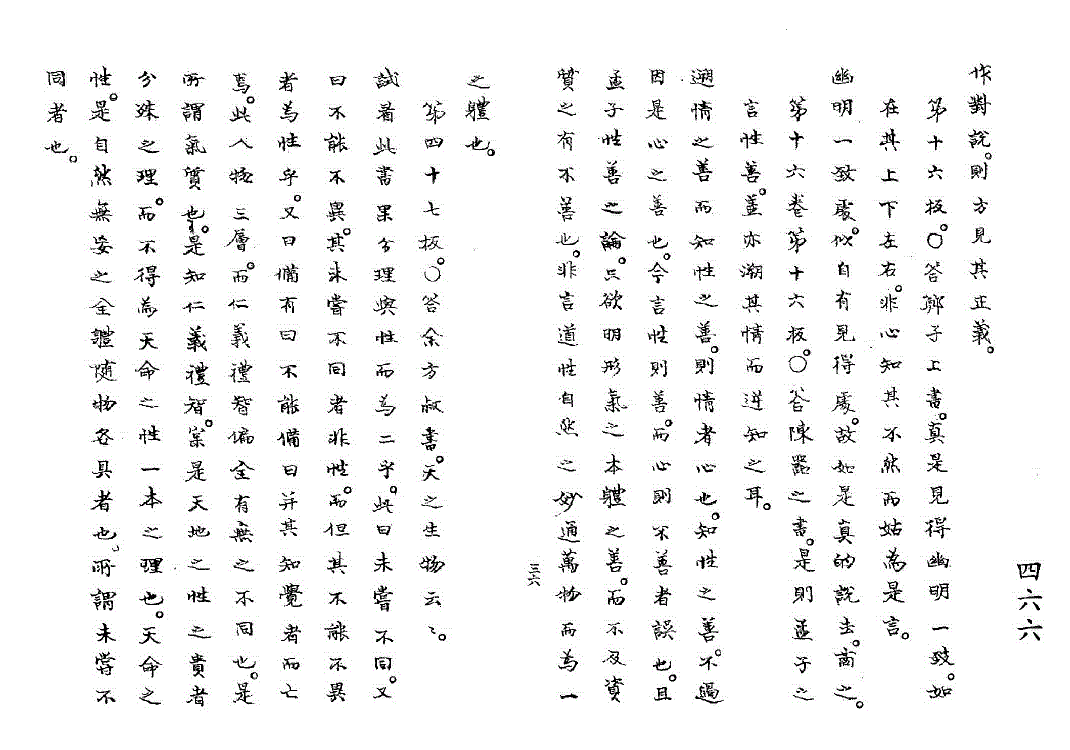 作对说。则方见其正义。
作对说。则方见其正义。第十六板○答郑子上书。真是见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为是言。
幽明一致处。似自有见得处。故如是真的说去。商之。
第十六卷第十六板○答陈器之书。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
溯情之善而知性之善。则情者心也。知性之善。不过因是心之善也。今言性则善。而心则不善者误也。且孟子性善之论。只欲明形气之本体之善。而不及资质之有不善也。非言道性自然之妙通万物而为一之体也。
第四十七板○答余方叔书。天之生物云云。
试看此书果分理与性而为二乎。此曰未尝不同。又曰不能不异。其未尝不同者非性。而但其不能不异者为性乎。又曰备有曰不能备曰并其知觉者而亡焉。此人物三层。而仁义礼智偏全有无之不同也。是所谓气质也。是知仁义礼智。宲是天地之性之贵者分殊之理。而不得为天命之性一本之理也。天命之性。是自然无妄之全体随物各具者也。所谓未尝不同者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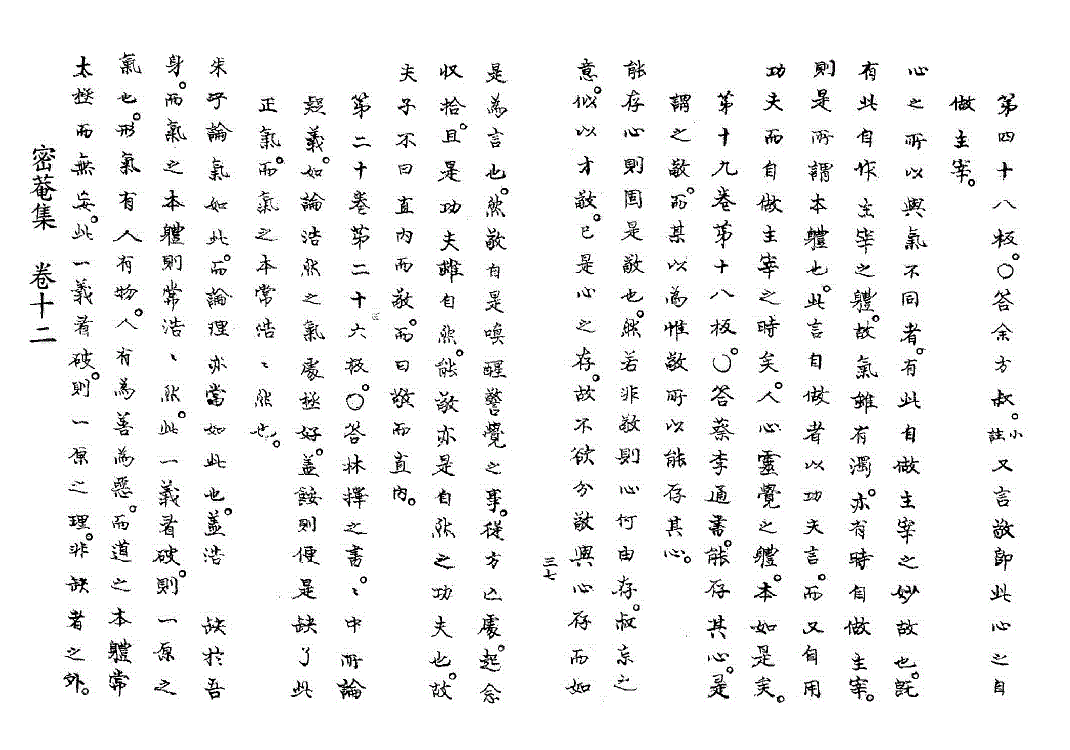 第四十八板○答余方叔。(小注)又言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
第四十八板○答余方叔。(小注)又言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心之所以与气不同者。有此自做主宰之妙故也。既有此自作主宰之体。故气虽有浊。亦有时自做主宰。则是所谓本体也。此言自做者以功夫言。而又自用功夫而自做主宰之时矣。人心灵觉之体。本如是矣。
第十九卷第十八板○答蔡李通书。能存其心。是谓之敬。而某以为惟敬所以能存其心。
能存心则固是敬也。然若非敬则心何由存。叔京之意。似以才敬。已是心之存。故不欲分敬与心存而如是为言也。然敬自是唤醒警觉之事。从方亡处。起念收拾。且是功夫虽自然。能敬亦是自然之功夫也。故夫子不曰直内而敬。而曰敬而直内。
第二十卷第二十六板○答林择之书。书中所论疑义。如论浩然之气处极好。盖馁则便是缺了此正气。而气之本常浩浩然也。
朱子论气如此。而论理亦当如此也。盖浩▣缺于吾身。而气之本体则常浩浩然。此一义看破。则一原之气也。形气有人有物。人有为善为恶。而道之本体常太极而无妄。此一义看破。则一原之理。非缺者之外。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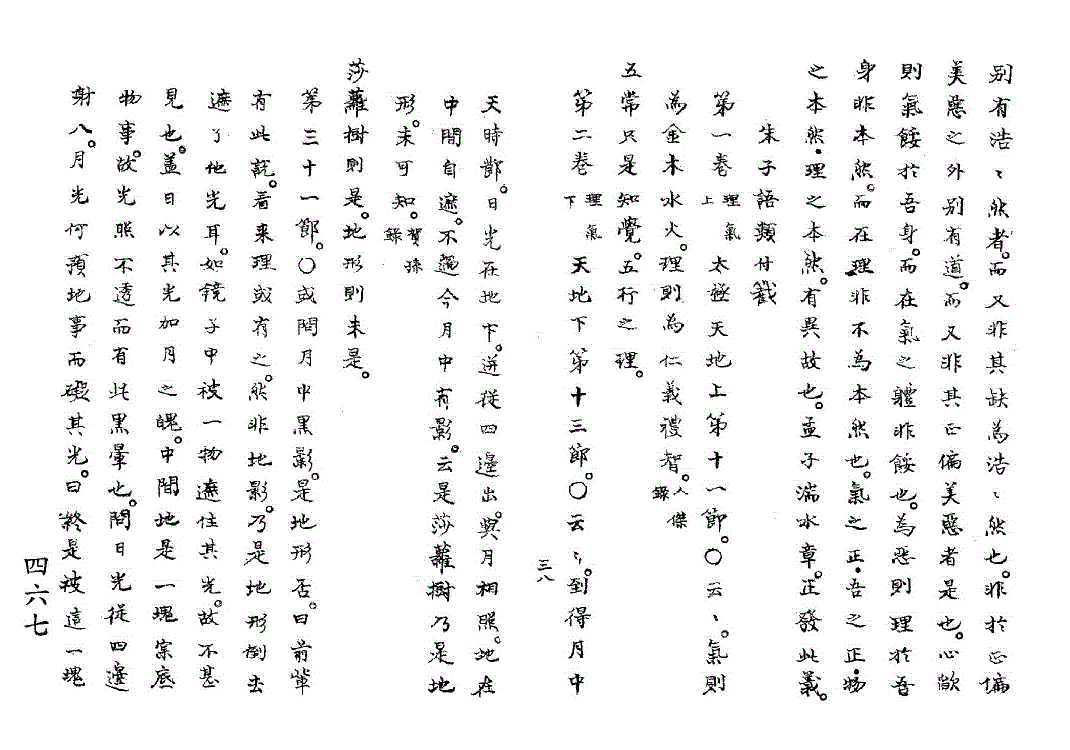 别有浩浩然者。而又非其缺为浩浩然也。非于正偏美恶之外别有道。而又非其正偏美恶者是也。心欿则气馁于吾身。而在气之体非馁也。为恶则理于吾身非本然。而在理非不为本然也。气之正,吾之正,物之本然,理之本然。有异故也。孟子湍水章。正发此义。
别有浩浩然者。而又非其缺为浩浩然也。非于正偏美恶之外别有道。而又非其正偏美恶者是也。心欿则气馁于吾身。而在气之体非馁也。为恶则理于吾身非本然。而在理非不为本然也。气之正,吾之正,物之本然,理之本然。有异故也。孟子湍水章。正发此义。朱子语类付签
第一卷(理气上)太极天地上第十一节○云云。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人杰录)
五常只是知觉。五行之理。
第二卷(理气下)天地下第十三节○云云。到得月中天时节。日光在地下。迸从四边出。与月相照。地在中间自遮。不过今月中有影。云是莎萝树乃是地形。未可知。(贺孙录)
莎萝树则是。地形则未是。
第三十一节○或问月中黑影。是地形否。曰前辈有此说。看来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镜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见也。盖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间地是一块宲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晕也。问日光从四边射入。月光何预地事而碍其光。曰终是被这一块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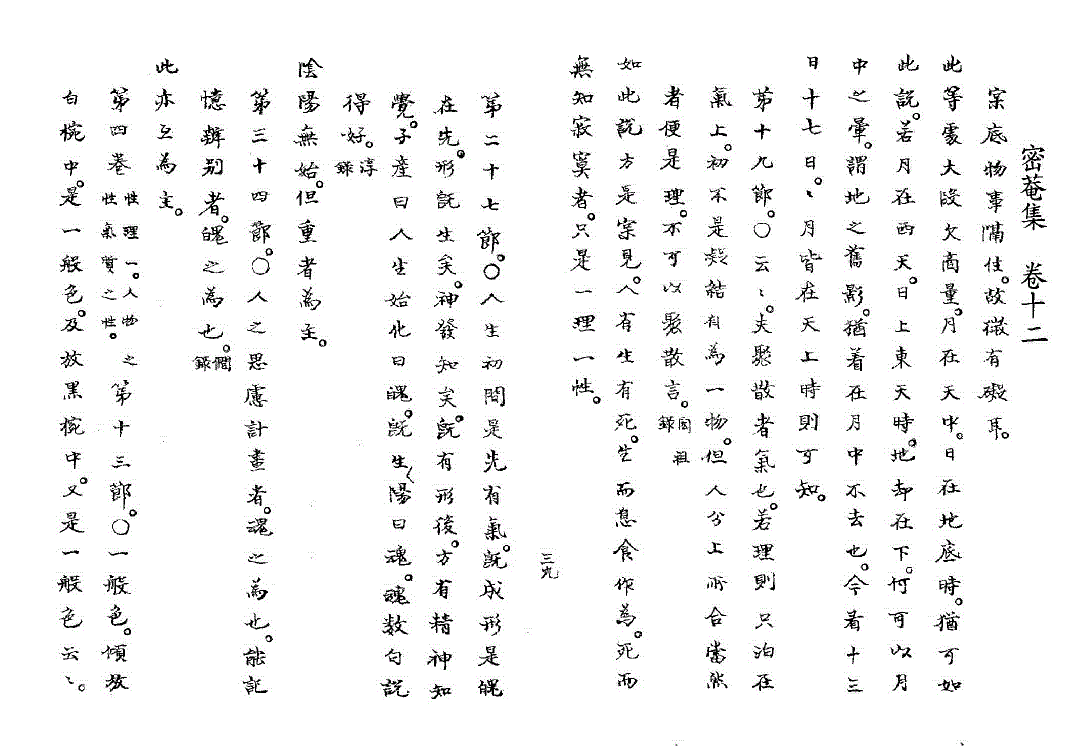 宲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碍耳。
宲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碍耳。此等处大段欠商量。月在天中。日在地底时。犹可如此说。若月在西天。日上东天时。地却在下。何可以月中之晕。谓地之旧影。犹着在月中不去也。今看十三日十七日。日月皆在天上时则可知。
第十九节○云云。夫聚散者气也。若理则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当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闳祖录)
如此说方是宲见。人有生有死。生而息食作为。死而无知寂寞者。只是一理一性。
第二十七节○人生初间是先有气。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一作魄)阳曰魂。数句说得好。(淳录)
阴阳无始。但重者为主。
第三十四节○人之思虑计画者。魂之为也。能记忆辨别者。魄之为也。(僩录)
此亦互为主。
第四卷(性理一。人物之性气质之性。)第十三节○一般色。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云云。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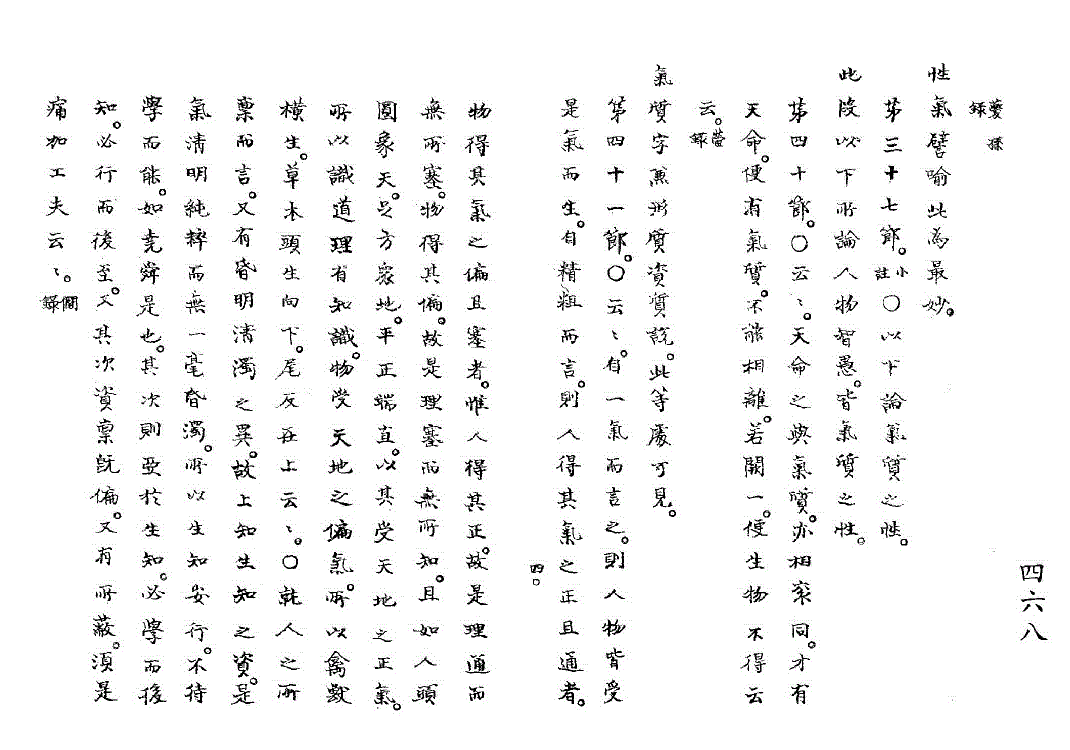 (夔孙录)
(夔孙录)性气譬喻此为最妙。
第三十七节。(小注)○以下论气质之性。
此段以下所论人物智愚。皆气质之性。
第四十节○云云。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云云。(㽦录)
气质字兼形质资质说。此等处可见。
第四十一节○云云。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象天。足方众(一作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云云。○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故上知生知之资。是气清明纯粹而无一毫昏浊。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学而能。如尧舜是也。其次则亚于生知。必学而后知。必行而后至。又其次资禀既偏。又有所蔽。须是痛加工夫云云。(僩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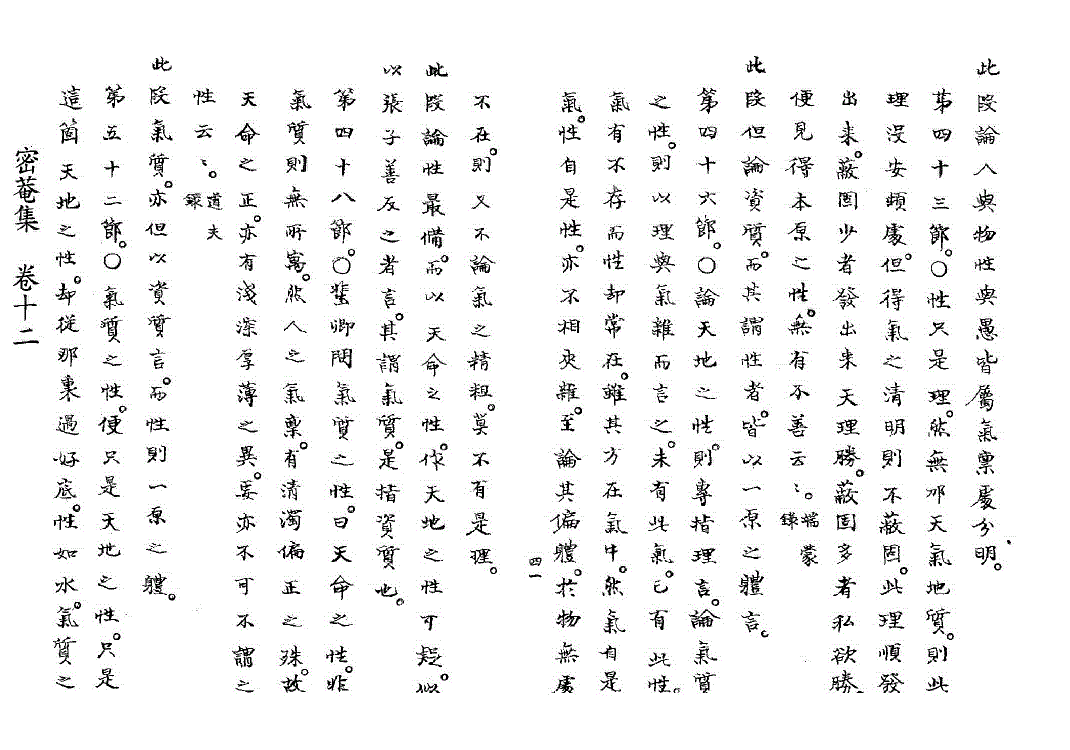 此段论人与物性与愚皆属气禀处分明。
此段论人与物性与愚皆属气禀处分明。第四十三节○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但得气之清明则不蔽固。此理顺发出来。蔽固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固多者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云云。(端蒙录)
此段但论资质。而其谓性者。皆以一原之体言。
第四十六节○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而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是气。性自是性。亦不相夹杂。至论其偏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
此段论性最备。而以天命之性。作天地之性可疑。似以张子善反之者言。其谓气质。是指资质也。
第四十八节○蜚卿问气质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寓。然人之气禀。有清浊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浅深厚薄之异。要亦不可不谓之性云云。(道夫录)
此段气质。亦但以资质言。而性则一原之体。
第五十二节○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好底。性如水。气质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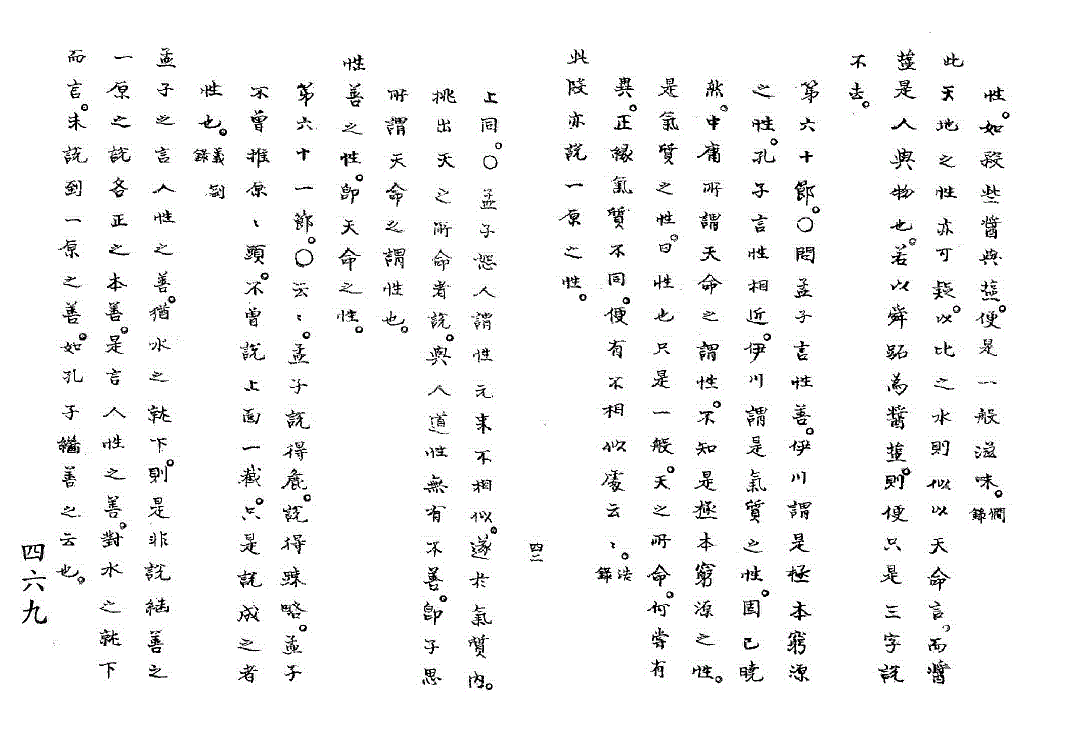 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僩录)
性。如杀些酱与盐。便是一般滋味。(僩录)此天地之性亦可疑。以比之水则似以天命言。而酱盐是人与物也。若以舜蹠为酱盐。则便只是三字说不去。
第六十节○问孟子言性善。伊川谓是极本穷源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谓是气质之性。固已晓然。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不知是极本穷源之性。是气质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尝有异。正缘气质不同。便有不相似处云云。(浩录)
此段亦说一原之性。
上同○孟子恕人谓性元来不相似。遂于气质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说。与人道性无有不善。即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也。
性善之性。即天命之性。
第六十一节○云云。孟子说得粗。说得疏略。孟子不曾推原原头。不曾说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义刚录)
孟子之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则是非说继善之一原之说各正之本善。是言人性之善。对水之就下而言。未说到一原之善。如孔子继善之云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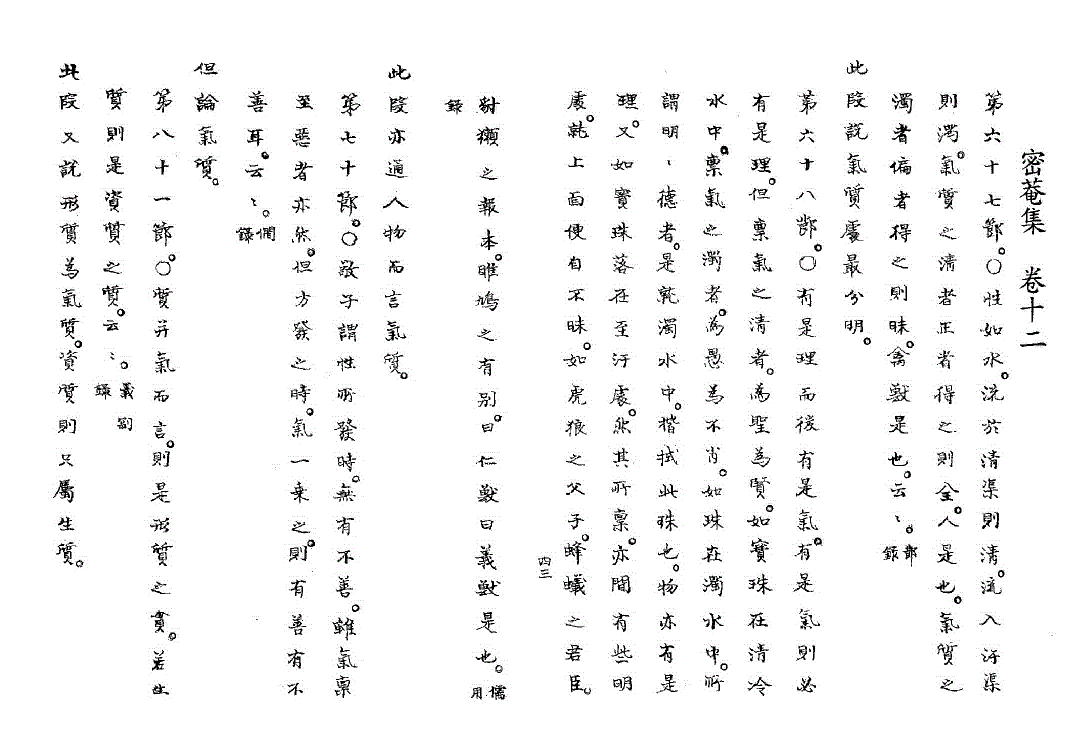 第六十七节○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云云。(节录)
第六十七节○性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入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云云。(节录)此段说气质处最分明。
第六十八节○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宝珠落在至污处。然其所禀。亦间有些明处。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儒用录)
此段亦通人物而言气质。
第七十节○敬子谓性所发时。无有不善。虽气禀至恶者亦然。但方发之时。气一乘之。则有善有不善耳。云云。(僩录)
但论气质。
第八十一节○质并气而言。则是形质之贯(一作质)。若生质则是资质之质。云云。(义刚录)
此段又说形质为气质。资质则只属生质。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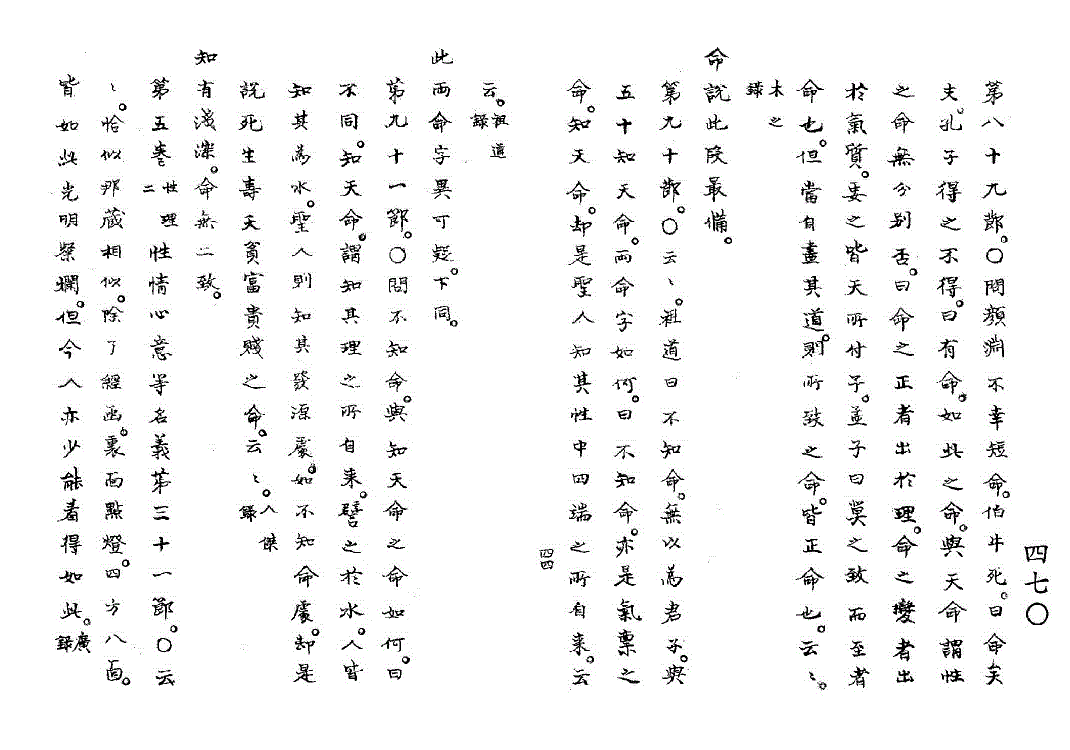 第八十九节○问颜渊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与天命谓性之命无分别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变者出于气质。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当自尽其道。则所致之命。皆正命也。云云。(木之录)
第八十九节○问颜渊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与天命谓性之命无分别否。曰命之正者出于理。命之变者出于气质。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当自尽其道。则所致之命。皆正命也。云云。(木之录)命说此段最备。
第九十节○云云。祖道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与五十知天命。两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气禀之命。知天命。却是圣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来。云云。(祖道录)
此两命字异可疑。下同。
第九十一节○问不知命。与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谓知其理之所自来。譬之于水。人皆知其为水。圣人则知其发源处。如不知命处。却是说死生寿夭贫富贵贱之命。云云。(人杰录)
知有浅深。命无二致。
第五卷(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第三十一节○云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经函。里面点灯。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烂。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广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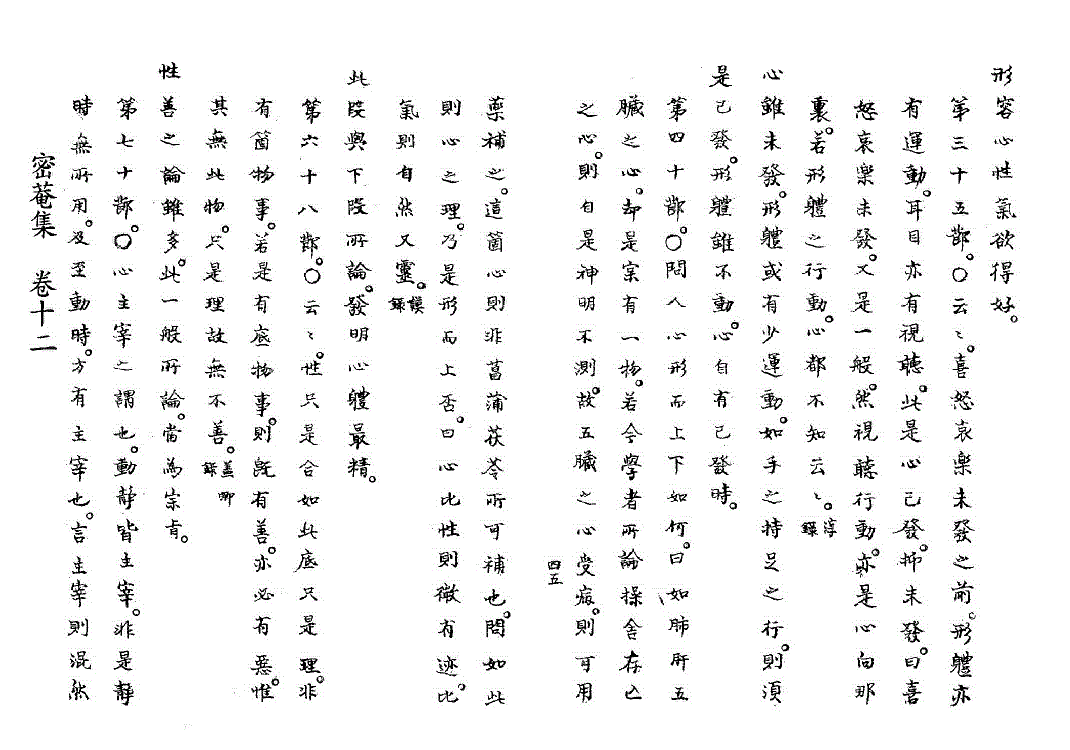 形容心性气欲得好。
形容心性气欲得好。第三十五节○云云。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形体亦有运动。耳目亦有视听。此是心已发。抑未发。曰喜怒哀乐未发。又是一般。然视听行动。亦是心向那里。若形体之行动。心都不知云云。(淳录)
心虽未发。形体或有少运动。如手之持足之行。则须是已发。形体虽不动。心自有已发时。
第四十节○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宲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问如此则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谟录)
此段与下段所论。发明心体最精。
第六十八节○云云。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若是有底物事。则既有善。亦必有恶。惟其无此物。只是理故无不善。(盖卿录)
性善之论虽多。此一般所论。当为宗旨。
第七十节○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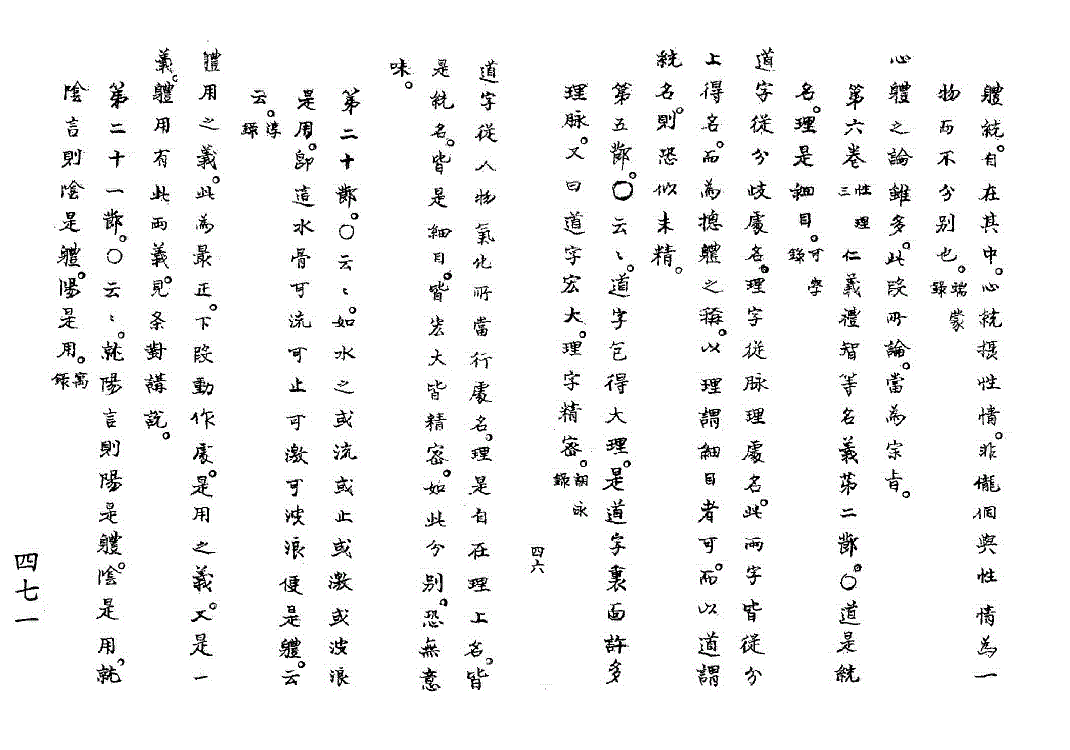 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端蒙录)
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端蒙录)心体之论虽多。此段所论。当为宗旨。
第六卷(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二节○道是统名。理是细目。(可学录)
道字从分歧处名。理字从脉理处名。此两字皆从分上得名。而为总体之称。以理谓细目者可。而以道谓统名。则恐似未精。
第五节○云云。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胡泳录)
道字从人物气化所当行处名。理是自在理上名。皆是统名。皆是细目。皆宏大皆精密。如此分别。恐无意味。
第二十节○云云。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或波浪是用。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可波浪便是体。云云。(淳录)
体用之义。此为最正。下段动作处。是用之义。又是一义。体用有此两义。见条对讲说。
第二十一节○云云。就阳言则阳是体。阴是用。就阴言则阴是体。阳是用。(寓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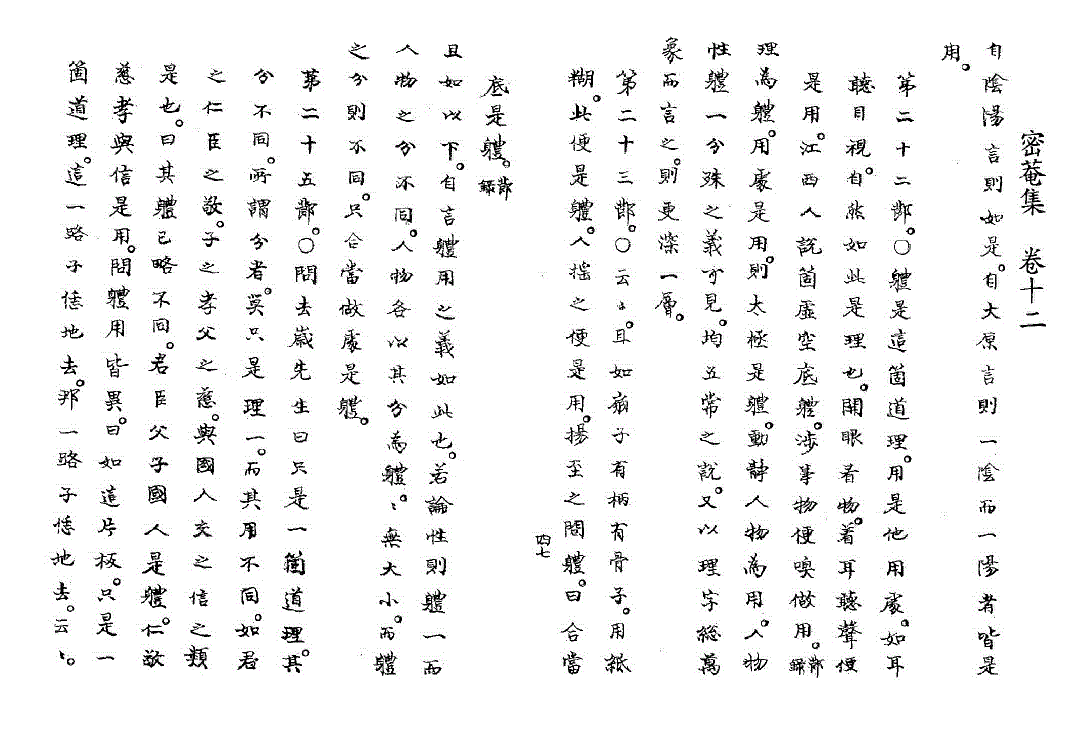 自阴阳言则如是。自大原言则一阴而一阳者皆是用。
自阴阳言则如是。自大原言则一阴而一阳者皆是用。第二十二节○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江西人说个虚空底体。涉事物便唤做用。(节录)
理为体。用处是用。则太极是体。动静人物为用。人物性体一分殊之义可见。均五常之说。又以理字总万象而言之。则更深一层。
第二十三节○云云。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纸糊。此便是体。人摇之便是用。扬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节录)
且如以下。自言体用之义如此也。若论性则体一而人物之分不同。人物各以其分为体。体无大小。而体之分则不同。只合当做处是体。
第二十五节○问去岁先生曰只是一个道理。其分不同。所谓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国人交之信之类是也。曰其体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国人是体。仁敬慈孝与信是用。问体用皆异。曰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云云。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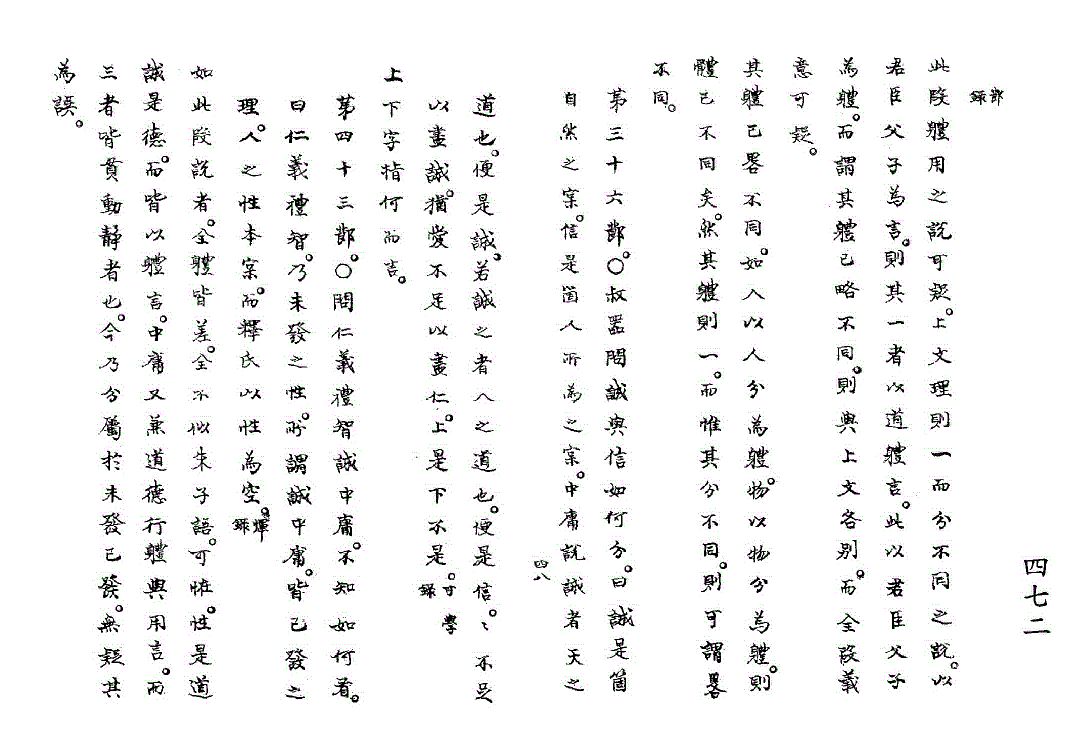 (节录)
(节录)此段体用之说可疑。上文理则一而分不同之说。以君臣父子为言。则其一者以道体言。此以君臣父子为体。而谓其体已略不同。则与上文各别。而全段义意可疑。
其体已略不同。如人以人分为体。物以物分为体。则体已不同矣。然其体则一。而惟其分不同。则可谓略不同。
第三十六节○叔器问诚与信如何分。曰诚是个自然之宲。信是个人所为之宲。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便是诚。若诚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上是下不是。(可学录)
上下字指何而言。
第四十三节○问仁义礼智诚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义礼智。乃未发之性。所谓诚中庸。皆已发之理。人之性本宲。而释氏以性为空。(煇录)
如此段说者。全体皆差。全不似朱子语。可怪。性是道诚是德。而皆以体言。中庸又兼道德行体与用言。而三者皆贯动静者也。今乃分属于未发已发。无疑其为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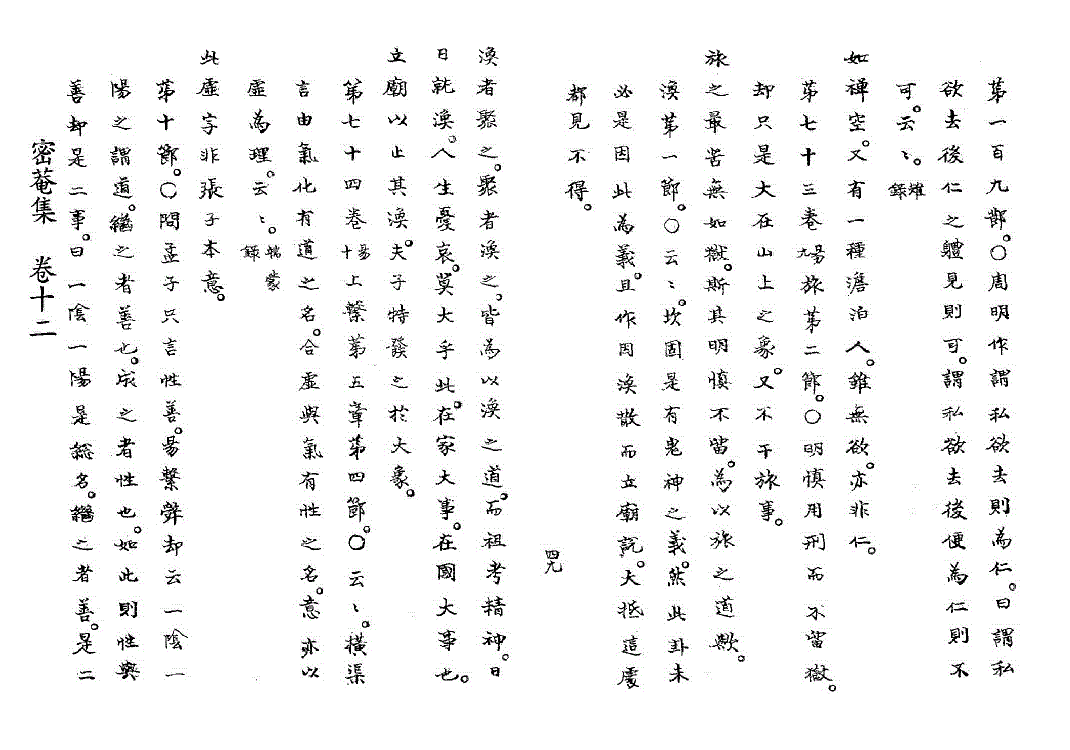 第一百九节○周明作谓私欲去则为仁。曰谓私欲去后仁之体见则可。谓私欲去后便为仁则不可。云云。(雉录)
第一百九节○周明作谓私欲去则为仁。曰谓私欲去后仁之体见则可。谓私欲去后便为仁则不可。云云。(雉录)如禅空。又有一种澹泊人。虽无欲。亦非仁。
第七十三卷(易九)旅第二节○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却只是大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旅之最苦无如狱。斯其明慎不留。为以旅之道欤。
涣第一节○云云。坎固是有鬼神之义。然此卦未必是因此为义。且作因涣散而立庙说。大抵这处都见不得。
涣者聚之。聚者涣之。皆为以涣之道。而祖考精神。日日就涣。人生忧哀。莫大乎此。在家大事。在国大事也。立庙以止其涣。夫子特发之于大象。
第七十四卷(易十)上系第五章第四节○云云。横渠言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意亦以虚为理。云云。(端蒙录)
此虚字非张子本意。
第十节○问孟子只言性善。易系辞却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则性与善却是二事。曰一阴一阳是总名。继之者善。是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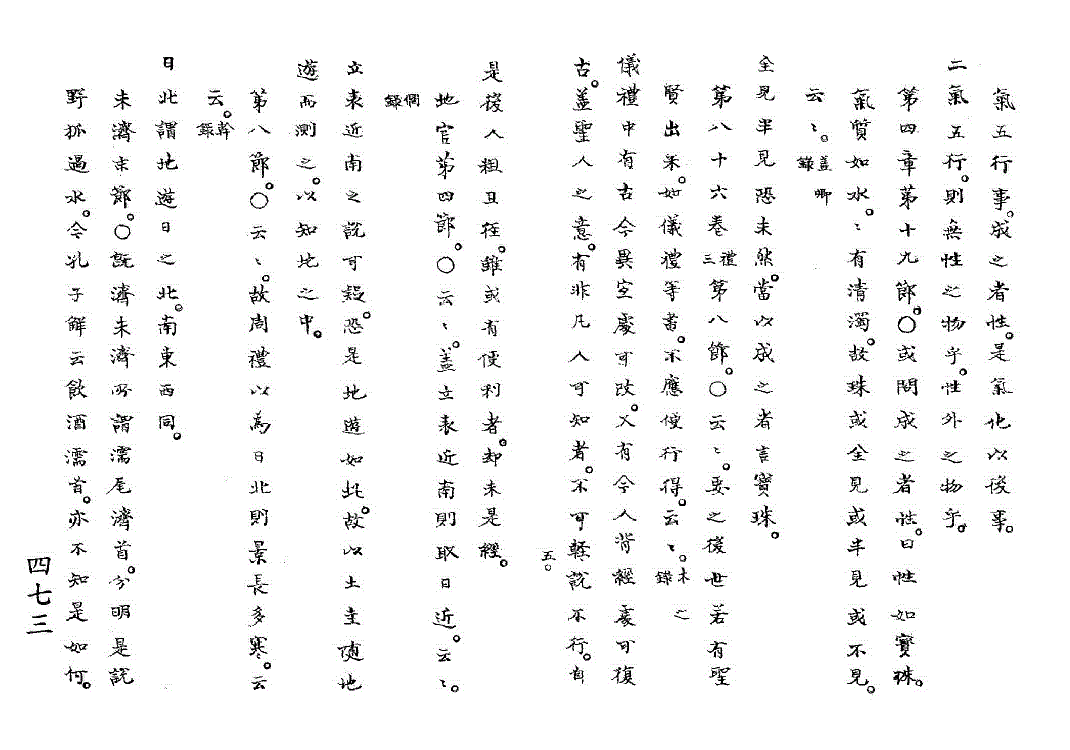 气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气化以后事。
气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气化以后事。二气五行。则无性之物乎。性外之物乎。
第四章第十九节○或问成之者性。曰性如宝珠。气质如水。水有清浊。故珠或全见或半见或不见。云云。(盖卿录)
全见半见恐未然。当以成之者言宝珠。
第八十六卷(礼三)第八节○云云。要之后世若有圣贤出来。如仪礼等书。不应便行得。云云。(木之录)
仪礼中有古今异宜处可改。又有今人背经处可复古。盖圣人之意。有非凡人可知者。不可轻说不行。自是后人粗且径。虽或有便利者。却未是经。
地官第四节○云云。盖立表近南则取日近。云云。(僩录)
立表近南之说可疑。恐是地游如此。故以土圭随地游而测之。以知地之中。
第八节○云云。故周礼以为日北则景长多寒。云云。(干录)
日北谓地游日之北。南东西同。
未济末节○既济未济所谓濡尾济首。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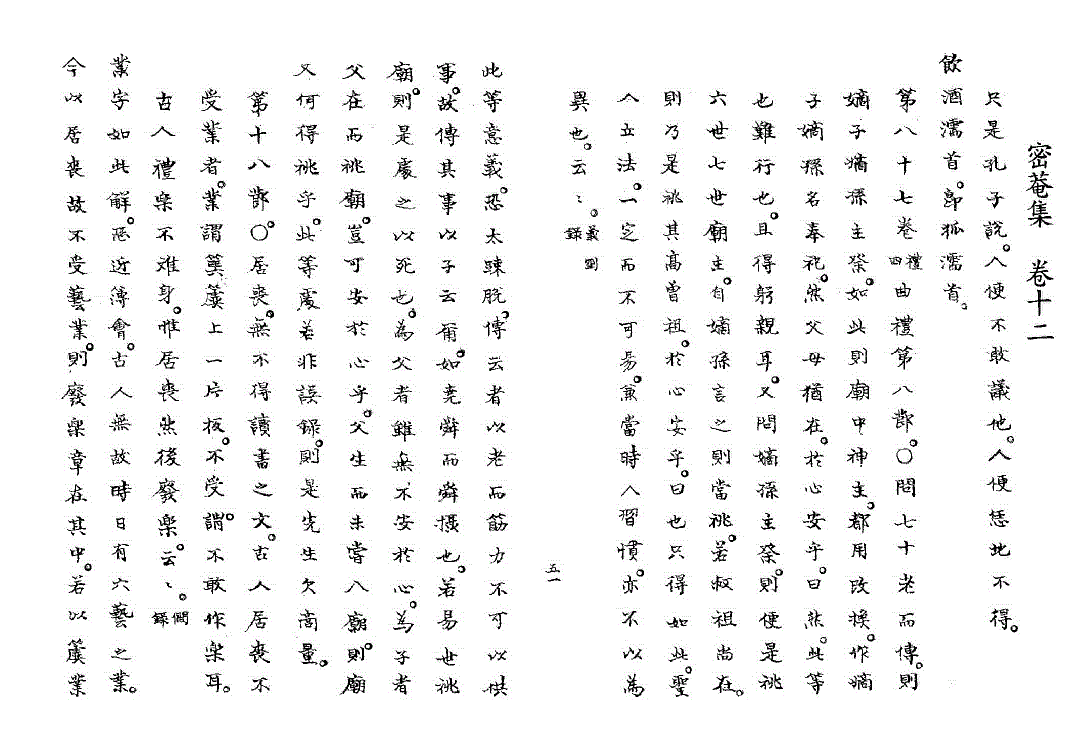 只是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
只是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饮酒濡首。即狐濡首。
第八十七卷(礼四)曲礼第八节○问七十老而传。则嫡子嫡孙主祭。如此则庙中神主。都用改换。作嫡子嫡孙名奉祀。然父母犹在。于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难行也。且得躬亲耳。又问嫡孙主祭。则便是祧六世七世庙主。自嫡孙言之则当祧。若叔祖尚在。则乃是祧其高曾祖。于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云云。(义刚录)
此等意义。恐太疏脱。传云者以老而筋力不可以供事。故传其事以子云尔。如尧舜而舜摄也。若易世祧庙。则是处之以死也。为父者虽无不安于心。为子者父在而祧庙。岂可安于心乎。父生而未尝入庙。则庙又何得祧乎。此等处若非误录。则是先生欠商量。
第十八节○居丧。无不得读书之文。古人居丧不受业者。业谓簨簴上一片板。不受。谓不敢作乐耳。古人礼乐不离身。惟居丧然后废乐。云云。(僩录)
业字如此解。恐近簿(一作傅)会。古人无故时日有六艺之业。今以居丧故不受艺业。则废乐章在其中。若以簴业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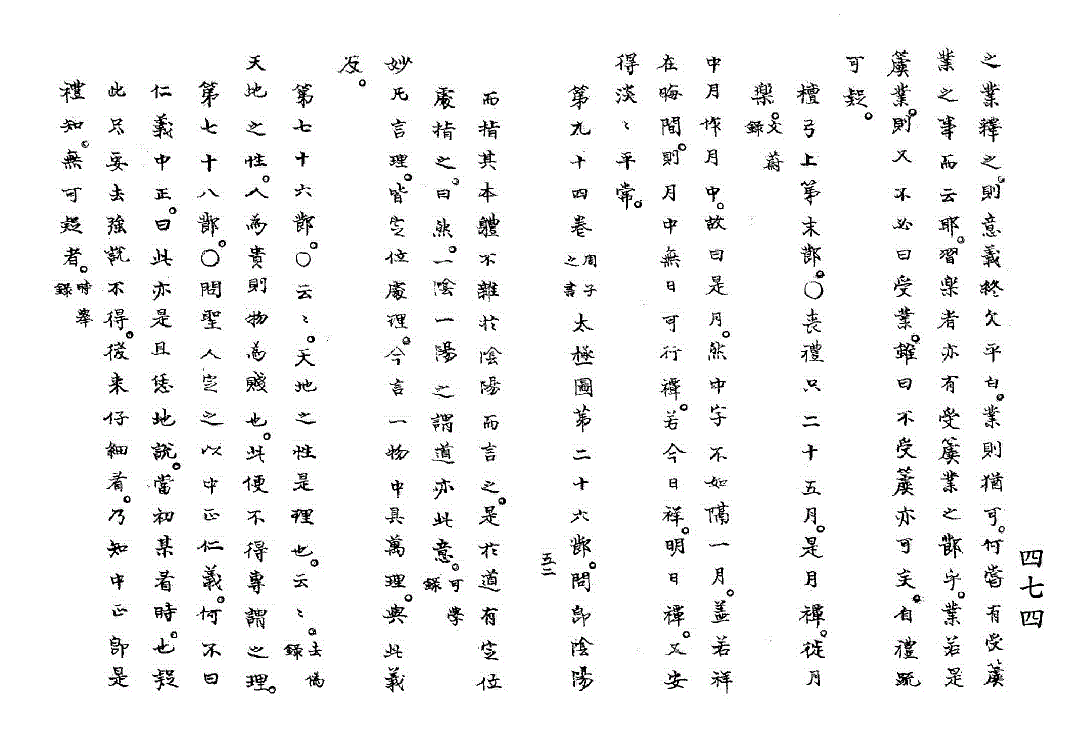 之业释之。则意义终欠平白。业则犹可。何尝有受簴业之事而云耶。习乐者亦有受簴业之节乎。业若是簴业。则又不必曰受业。虽曰不受簴亦可矣。自礼疏可疑。
之业释之。则意义终欠平白。业则犹可。何尝有受簴业之事而云耶。习乐者亦有受簴业之节乎。业若是簴业。则又不必曰受业。虽曰不受簴亦可矣。自礼疏可疑。檀弓上第末节○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乐。(文蔚录)
中月作月中。故曰是月。然中字不如隔一月。盖若祥在晦间。则月中无日可行禫。若今日祥。明日禫。又安得淡淡平常。
第九十四卷(周子之书)太极图第二十六节○问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于阴阳而言之。是于道有定位处指之。曰然。一阴一阳之谓道亦此意。(可学录)
妙凡言理。皆定位处理。今言一物中具万理。与此义反。
第七十六节○云云。天地之性是理也。云云。(去伪录)
天地之性。人为贵则物为贱也。此便不得专谓之理。
第七十八节○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何不曰仁义中正。曰此亦是且恁地说。当初某看时。也疑此只要去强说不得。后来仔细看。乃知中正即是礼知。无可疑者。(时举录)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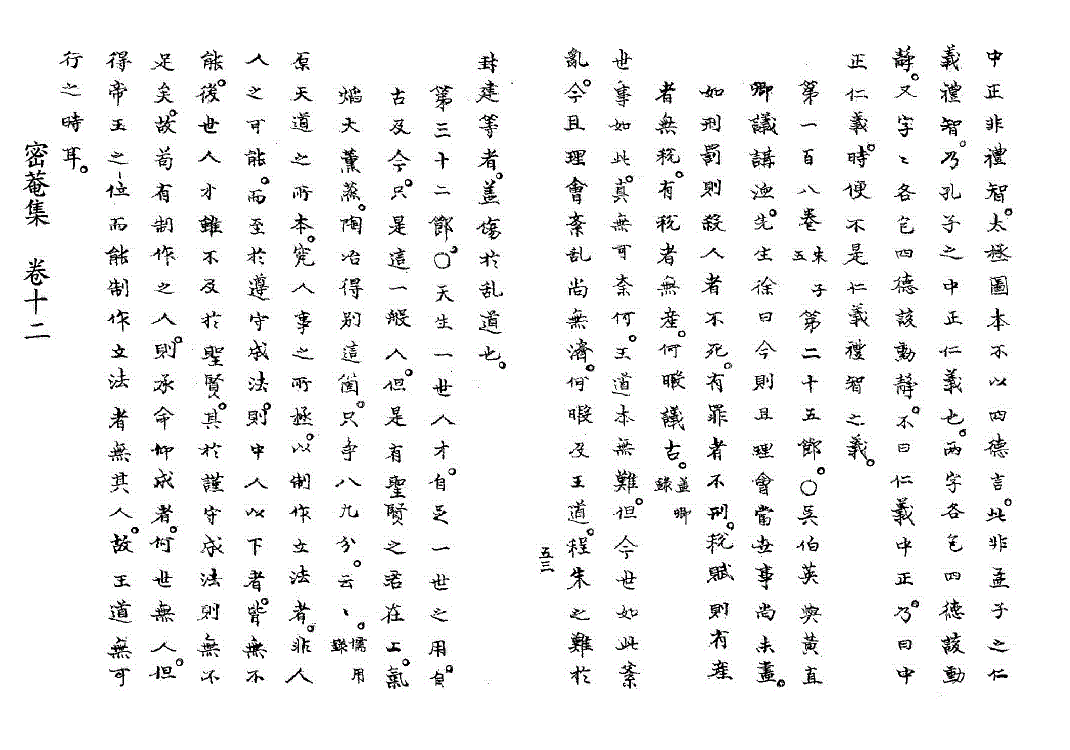 中正非礼智。太极图本不以四德言。此非孟子之仁义礼智。乃孔子之中正仁义也。两字各包四德该动静。又字字各包四德该动静。不曰仁义中正。乃曰中正仁义。时便不是仁义礼智之义。
中正非礼智。太极图本不以四德言。此非孟子之仁义礼智。乃孔子之中正仁义也。两字各包四德该动静。又字字各包四德该动静。不曰仁义中正。乃曰中正仁义。时便不是仁义礼智之义。第一百八卷(朱子五)第二十五节○吴伯英与黄直卿议讲(一作沟)洫。先生徐曰今则且理会当世事尚未尽。如刑罚则杀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税赋则有产者无税。有税者无产。何暇议古。(盖卿录)
世事如此。真无可奈何。王道本无难。但今世如此紊乱。今且理会紊乱尚无济。何暇及王道。程朱之难于封建等者。盖伤于乱道也。
第三十二节○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这一般人。但是有圣贤之君在上。气焰大薰蒸。陶冶得别这个。只争八九分。云云。(儒用录)
原天道之所本。究人事之所极。以制作立法者。非人人之可能。而至于遵守成法。则中人以下者。皆无不能。后世人才虽不及于圣贤。其于谨守成法则无不足矣。故苟有制作之人。则承命仰成者。何世无人。但得帝王之位而能制作立法者无其人。故王道无可行之时耳。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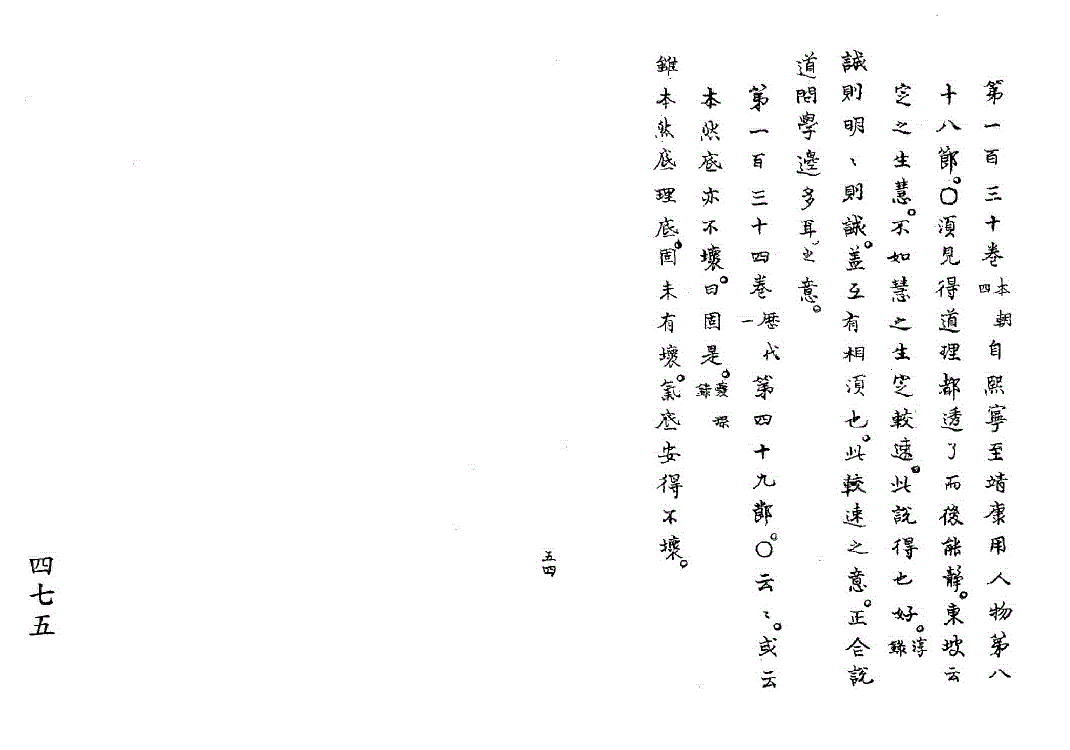 第一百三十卷(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物第八十八节○须见得道理都透了而后能静。东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较速。此说得也好。(淳录)
第一百三十卷(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物第八十八节○须见得道理都透了而后能静。东坡云定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较速。此说得也好。(淳录)诚则明明则诚。盖互有相须也。此较速之意。正合说道问学边多耳之意。
第一百三十四卷(历代一)第四十九节○云云。或云本然底亦不坏。曰固是。(夔孙录)
虽本然底理底。固未有坏。气底安得不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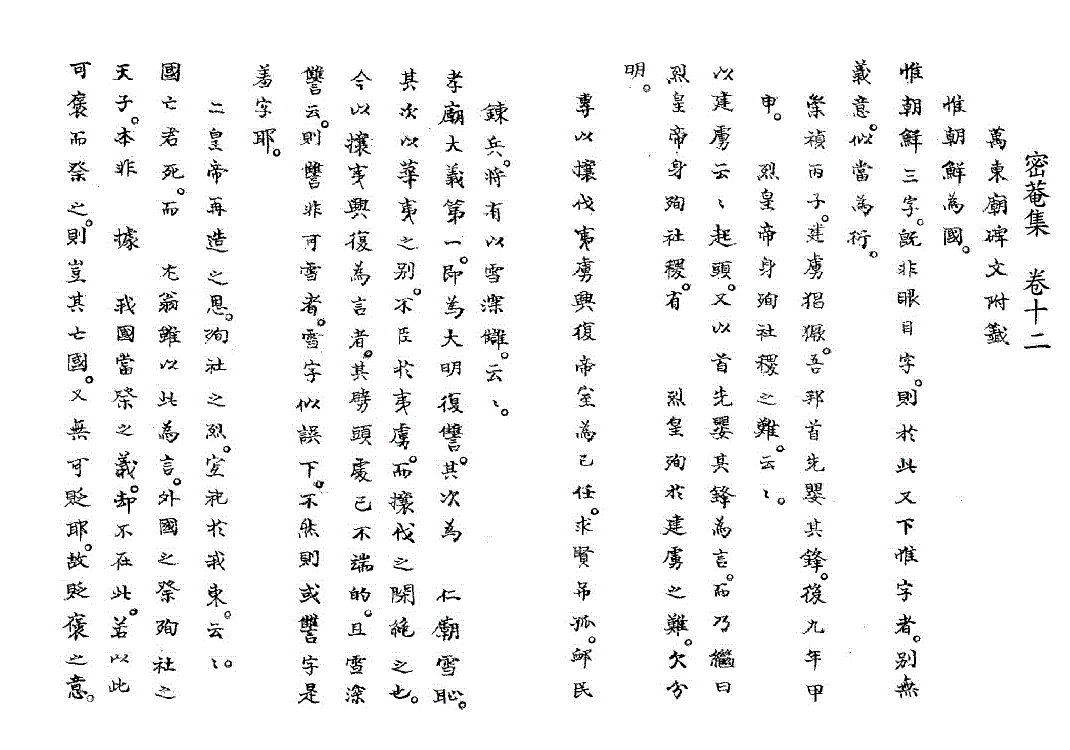 万东庙碑文附签
万东庙碑文附签惟朝鲜为国。
惟朝鲜三字。既非眼目字。则于此又下惟字者。别无义意。似当为衍。
崇祯丙子。建虏猖獗。吾邦首先婴其锋。后九年甲申。 烈皇帝身殉社稷之难。云云。
以建虏云云起头。又以首先婴其锋为言。而乃继曰烈皇帝身殉社稷。有 烈皇殉于建虏之难。欠分明。
专以攘伐夷虏兴复帝室为己任。求贤吊孤。恤民鍊兵。将有以雪深雠。云云。
孝庙大义第一。即为大明复雠。其次为 仁庙雪耻。其次以华夷之别。不臣于夷虏。而攘伐之闭绝之也。今以攘夷兴复为言者。其劈头处已不端的。且雪深雠云。则雠非可雪者。雪字似误下。不然则或雠字是羞字耶。
二皇帝再造之恩。殉社之烈。宜祀于我东。云云。
国亡君死。而 尤翁虽以此为言。外国之祭殉社之天子。本非 据 我国当祭之义。却不在此。若以此可褒而祭之。则岂其亡国。又无可贬耶。故贬褒之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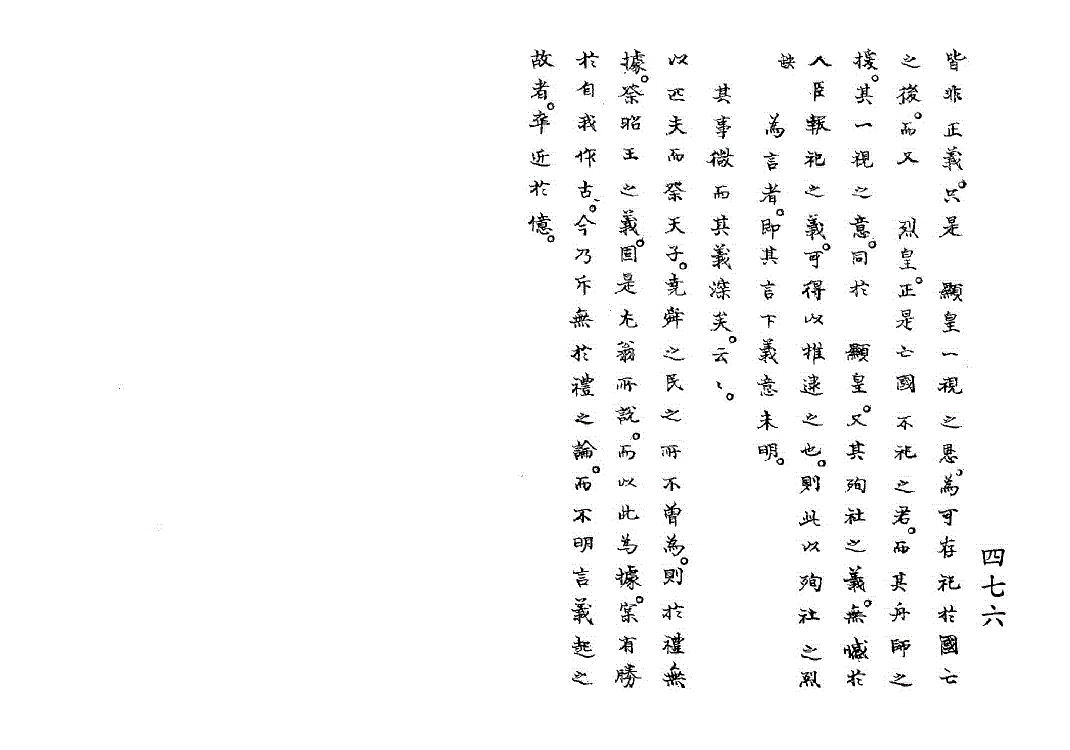 皆非正义。只是 显皇一视之恩。为可存祀于国亡之后。而又 烈皇。正是亡国不祀之君。而其舟师之援。其一视之意。同于 显皇。又其殉社之义。无憾于人臣报祀之义。可得以推逮之也。则此以殉社之烈(缺)为言者。即其言下义意未明。
皆非正义。只是 显皇一视之恩。为可存祀于国亡之后。而又 烈皇。正是亡国不祀之君。而其舟师之援。其一视之意。同于 显皇。又其殉社之义。无憾于人臣报祀之义。可得以推逮之也。则此以殉社之烈(缺)为言者。即其言下义意未明。其事微而其义深矣。云云。
以匹夫而祭天子。尧舜之民之所不曾为。则于礼无据。祭昭王之义。固是尤翁所说。而以此为据。宲有胜于自我作古。今乃斥无于礼之论。而不明言义起之故者。卒近于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