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杂著
杂著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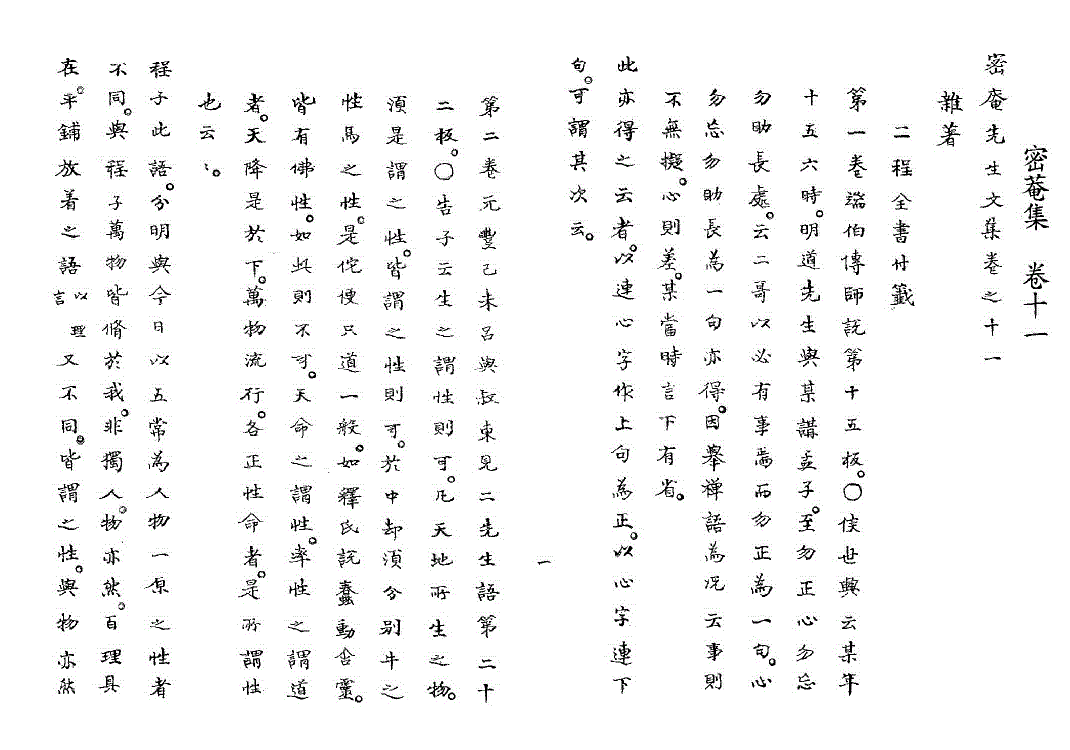 二程全书付签
二程全书付签第一卷端伯传师说第十五板○侯世兴云某年十五六时。明道先生与某讲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亦得。因举禅语况云事则不无拟。心则差。某当时言下有省。
此亦得之云者。以连心字作上句为正。以心字连下句。可谓其次云。
第二卷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第二十二板○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佗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云云。
程子此语。分明与今日以五常为人物一原之性者不同。与程子万物皆脩于我。非独人。物亦然。百理具在。平铺放着之语(以理言)又不同。皆谓之性。与物亦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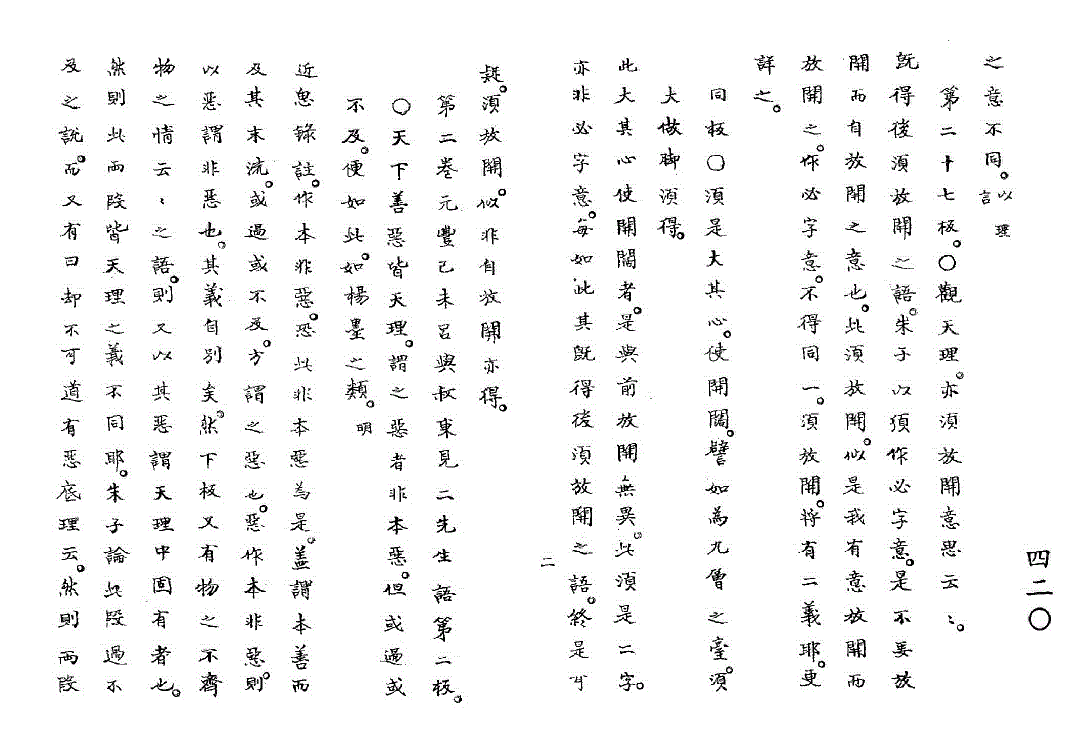 之意不同。(以理言)
之意不同。(以理言)第二十七板○观天理。亦须放开意思云云。
既得后须放开之语。朱子以须作必字意。是不要放开而自放开之意也。此须放开。似是我有意放开而放开之。作必字意。不得同一。须放开。将有二义耶。更详之。
同板○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须得。
此大其心使开阔者。是与前放开无异。此须是二字。亦非必字意。每如此其既得后须放开之语。终是可疑。须放开。似非自放开亦得。
第二卷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第二板○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明)
近思录注。作本非恶。恐此非本恶为是。盖谓本善而及其末流。或过或不及。方谓之恶也。恶作本非恶。则以恶谓非恶也。其义自别矣。然下板又有物之不齐物之情云云之语。则又以其恶谓天理中固有者也。然则此两段皆天理之义不同耶。朱子论此段过不及之说。而又有曰却不可道有恶底理云。然则两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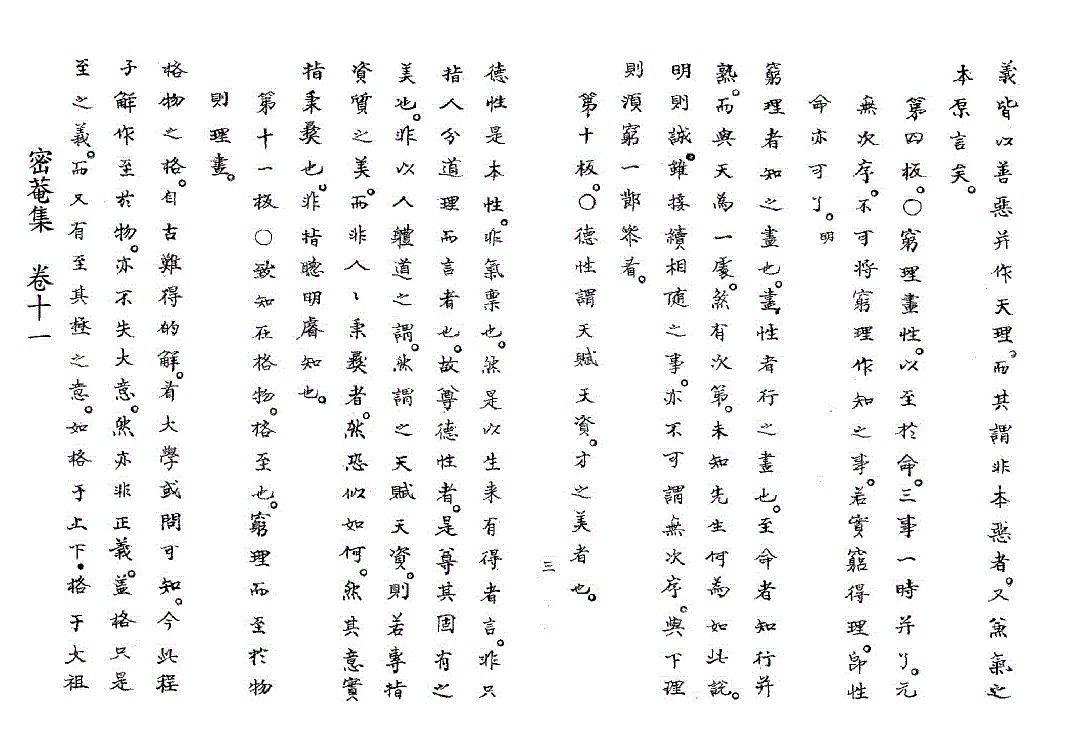 义皆以善恶并作天理。而其谓非本恶者。又兼气之本原言矣。
义皆以善恶并作天理。而其谓非本恶者。又兼气之本原言矣。第四板○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
穷理者知之尽也。尽性者行之尽也。至命者知行并熟。而与天为一处。煞有次第。未知先生何为如此说。明则诚。虽接续相随之事。亦不可谓无次序。与下理则须穷一节参看。
第十板○德性谓天赋天资。才之美者也。
德性是本性。非气禀也。然是以生来有得者言。非只指人分道理而言者也。故尊德性者。是尊其固有之美也。非以人体道之谓。然谓之天赋天资。则若专指资质之美。而非人人秉彝者。然恐似如何。然其意实指秉彝也。非指聪明睿知也。
第十一板○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理尽。
格物之格。自古难得的解。看大学或问可知。今此程子解作至于物。亦不失大意。然亦非正义。盖格只是至之义。而又有至其极之意。如格于上下,格于文祖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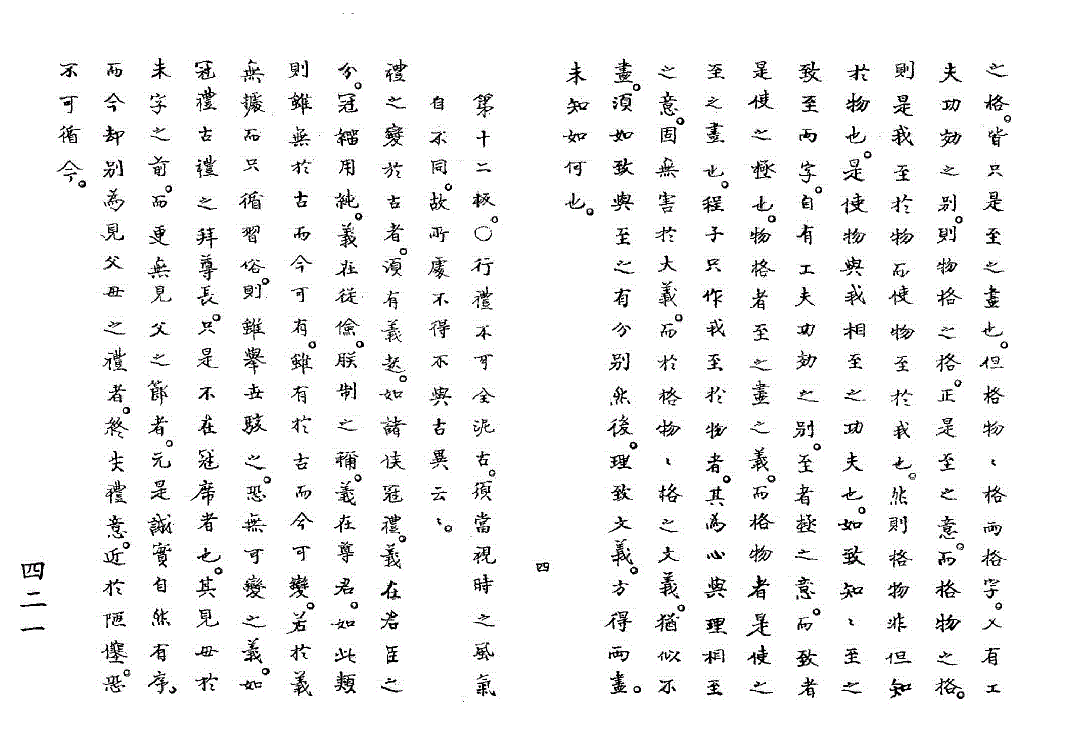 之格。皆只是至之尽也。但格物物格两格字。又有工夫功效之别。则物格之格。正是至之意。而格物之格。则是我至于物而使物至于我也。然则格物非但知于物也。是使物与我相至之功夫也。如致知知至之致至两字。自有工夫功效之别。至者极之意。而致者是使之极也。物格者至之尽之义。而格物者是使之至之尽也。程子只作我至于物者。其为心与理相至之意。固无害于大义。而于格物物格之文义。犹似不尽。须如致与至之有分别然后。理致文义。方得两尽。未知如何也。
之格。皆只是至之尽也。但格物物格两格字。又有工夫功效之别。则物格之格。正是至之意。而格物之格。则是我至于物而使物至于我也。然则格物非但知于物也。是使物与我相至之功夫也。如致知知至之致至两字。自有工夫功效之别。至者极之意。而致者是使之极也。物格者至之尽之义。而格物者是使之至之尽也。程子只作我至于物者。其为心与理相至之意。固无害于大义。而于格物物格之文义。犹似不尽。须如致与至之有分别然后。理致文义。方得两尽。未知如何也。第十二板○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云云。
礼之变于古者。须有义起。如诸侯冠礼。义在君臣之分。冠𦃓用纯。义在从俭。朕制之称。义在尊君。如此类则虽无于古而今可有。虽有于古而今可变。若于义无据而只循习俗。则虽举世骇之。恐无可变之义。如冠礼古礼之拜尊长。只是不在冠席者也。其见母于未字之前。而更无见父之节者。元是诚实自然有序。而今却别为见父母之礼者。终失礼意。近于陋僿。恐不可循今。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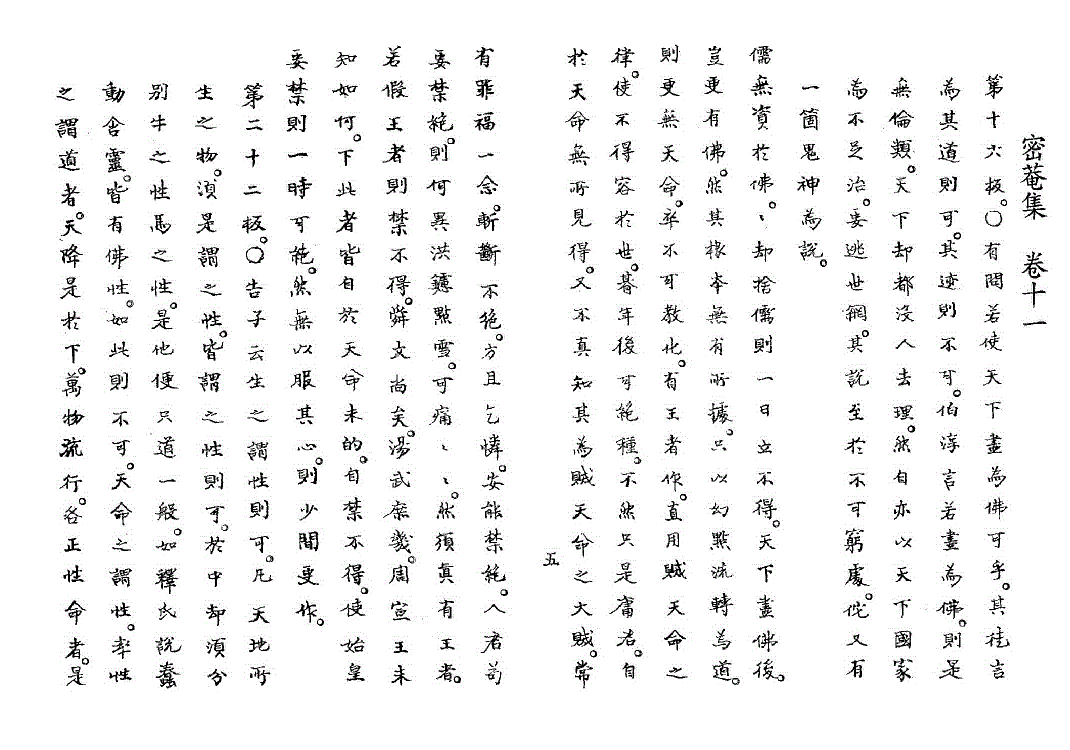 第十六板○有问若使天下尽为佛可乎。其徒言为其道则可。其迹则不可。伯淳言若尽为佛。则是无伦类。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国家为不足治。要逃世网。其说至于不可穷处。佗又有一个鬼神为说。
第十六板○有问若使天下尽为佛可乎。其徒言为其道则可。其迹则不可。伯淳言若尽为佛。则是无伦类。天下却都没人去理。然自亦以天下国家为不足治。要逃世网。其说至于不可穷处。佗又有一个鬼神为说。儒无资于佛。佛却舍儒则一日立不得。天下尽佛后。岂更有佛。然其根本无有所据。只以幻点流转为道。则更无天命。卒不可教化。有王者作。直用贼天命之律。使不得容于世。期年后可绝种。不然只是庸君。自于天命无所见得。又不真知其为贼天命之大贼。常有罪福一念。斩断不绝。方且乞怜。安能禁绝。人君苟要禁绝。则何异洪铝点雪。可痛可痛。然须真有王者。若假王者则禁不得。舜文尚矣。汤武庶几。周宣王未知如何。下此者皆自于天命未的。自禁不得。使始皇要禁则一时可绝。然无以服其心。则少间更作。
第二十二板○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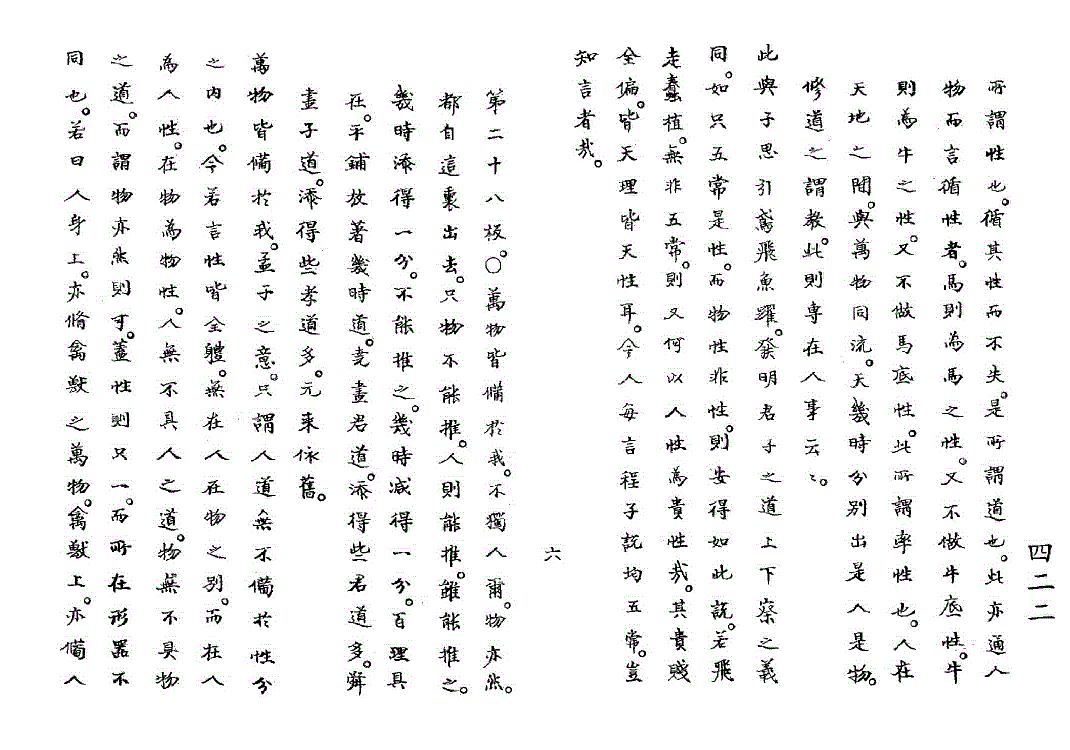 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云云。
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做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云云。此与子思引鸢飞鱼跃。发明君子之道上下察之义同。如只五常是性。而物性非性。则安得如此说。若飞走蠢植。无非五常。则又何以人性为贵性哉。其贵贱全偏。皆天理皆天性耳。今人每言程子说均五常。岂知言者哉。
第二十八板○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亦然。都自这里出去。只物不能推。人则能推。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著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来依旧。
万物皆备于我。孟子之意。只谓人道无不备于性分之内也。今若言性皆全体。无在人在物之别。而在人为人性。在物为物性。人无不具人之道。物无不具物之道。而谓物亦然则可。盖性则只一。而所在形器不同也。若曰人身上。亦脩禽兽之万物。禽兽上。亦备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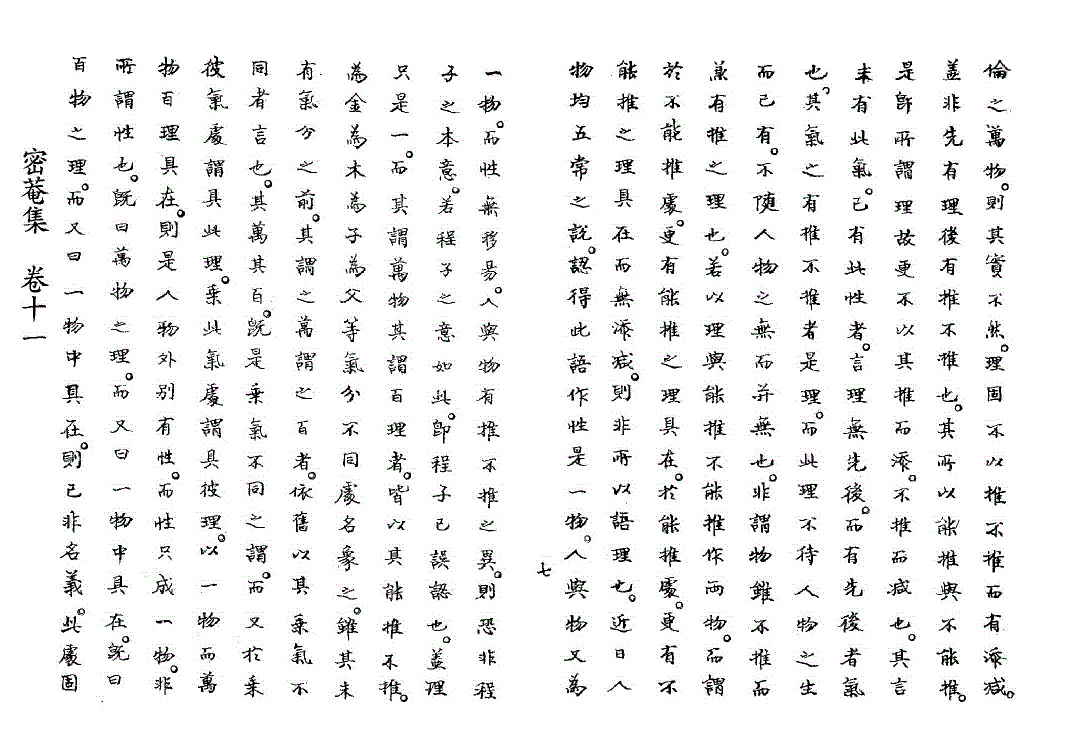 伦之万物。则其实不然。理固不以推不推而有添减。盖非先有理后有推不推也。其所以能推与不能推。是即所谓理故更不以其推而添。不推而减也。其言未有此气。已有此性者。言理无先后。而有先后者气也。其气之有推不推者是理。而此理不待人物之生而已有。不随人物之无而并无也。非谓物虽不推而兼有推之理也。若以理与能推不能推作两物。而谓于不能推处。更有能推之理具在。于能推处。更有不能推之理具在而无添减。则非所以语理也。近日人物均五常之说。认得此语作性是一物。人与物又为一物。而性无移易。人与物有推不推之异。则恐非程子之本意。若程子之意如此。即程子已误认也。盖理只是一。而其谓万物其谓百理者。皆以其能推不推。为金为木为子为父等气分不同处名象之。虽其未有气分之前。其谓之万谓之百者。依旧以其乘气不同者言也。其万其百。既是乘气不同之谓。而又于乘彼气处谓具此理。乘此气处谓具彼理。以一物而万物百理具在。则是人物外别有性。而性只成一物。非所谓性也。既曰万物之理。而又曰一物中具在。既曰百物之理。而又曰一物中具在。则已非名义。此处固
伦之万物。则其实不然。理固不以推不推而有添减。盖非先有理后有推不推也。其所以能推与不能推。是即所谓理故更不以其推而添。不推而减也。其言未有此气。已有此性者。言理无先后。而有先后者气也。其气之有推不推者是理。而此理不待人物之生而已有。不随人物之无而并无也。非谓物虽不推而兼有推之理也。若以理与能推不能推作两物。而谓于不能推处。更有能推之理具在。于能推处。更有不能推之理具在而无添减。则非所以语理也。近日人物均五常之说。认得此语作性是一物。人与物又为一物。而性无移易。人与物有推不推之异。则恐非程子之本意。若程子之意如此。即程子已误认也。盖理只是一。而其谓万物其谓百理者。皆以其能推不推。为金为木为子为父等气分不同处名象之。虽其未有气分之前。其谓之万谓之百者。依旧以其乘气不同者言也。其万其百。既是乘气不同之谓。而又于乘彼气处谓具此理。乘此气处谓具彼理。以一物而万物百理具在。则是人物外别有性。而性只成一物。非所谓性也。既曰万物之理。而又曰一物中具在。既曰百物之理。而又曰一物中具在。则已非名义。此处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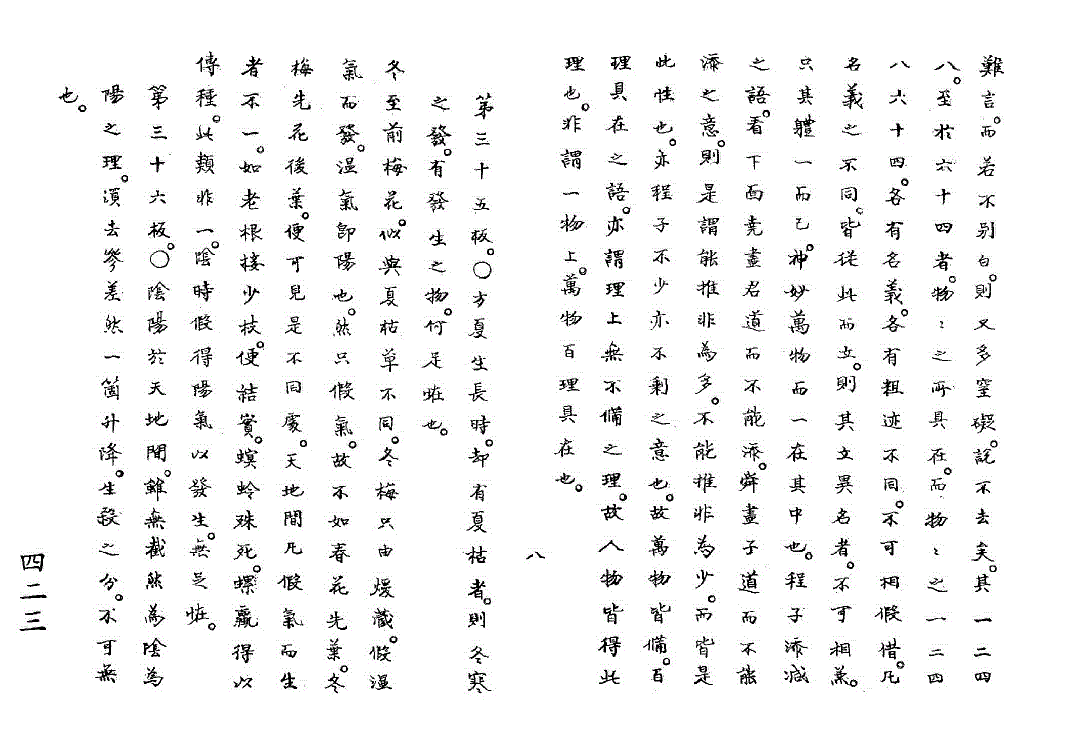 难言。而若不别白。则又多窒碍。说不去矣。其一二四八。至于六十四者。物物之所具在。而物物之一二四八六十四。各有名义。各有粗迹不同。不可相假借。凡名义之不同。皆从此而立。则其立异名者。不可相兼。只其体一而已。神妙万物而一在其中也。程子添减之语。着下面尧尽君道而不能添。舜尽子道而不能添之意。则是谓能推非为多。不能推非为少。而皆是此性也。亦程子不少亦不剩之意也。故万物皆备。百理具在之语。亦谓理上无不备之理。故人物皆得此理也。非谓一物上。万物百理具在也。
难言。而若不别白。则又多窒碍。说不去矣。其一二四八。至于六十四者。物物之所具在。而物物之一二四八六十四。各有名义。各有粗迹不同。不可相假借。凡名义之不同。皆从此而立。则其立异名者。不可相兼。只其体一而已。神妙万物而一在其中也。程子添减之语。着下面尧尽君道而不能添。舜尽子道而不能添之意。则是谓能推非为多。不能推非为少。而皆是此性也。亦程子不少亦不剩之意也。故万物皆备。百理具在之语。亦谓理上无不备之理。故人物皆得此理也。非谓一物上。万物百理具在也。第三十五板○方夏生长时。却有夏枯者。则冬寒之发。有发生之物。何足怪也。
冬至前梅花。似与夏枯草不同。冬梅只由煖藏。假温气而发。温气即阳也。然只假气。故不如春花先叶。冬梅先花后叶。便可见是不同处。天地间凡假气而生者不一。如老根接少枝。便结实。螟蛉殊死。螺蠃得以传种。此类非一。阴时假得阳气以发生。无足怪。
第三十六板○阴阳于天地间。虽无截然为阴为阳之理。须去参差然一个升降。生杀之分。不可无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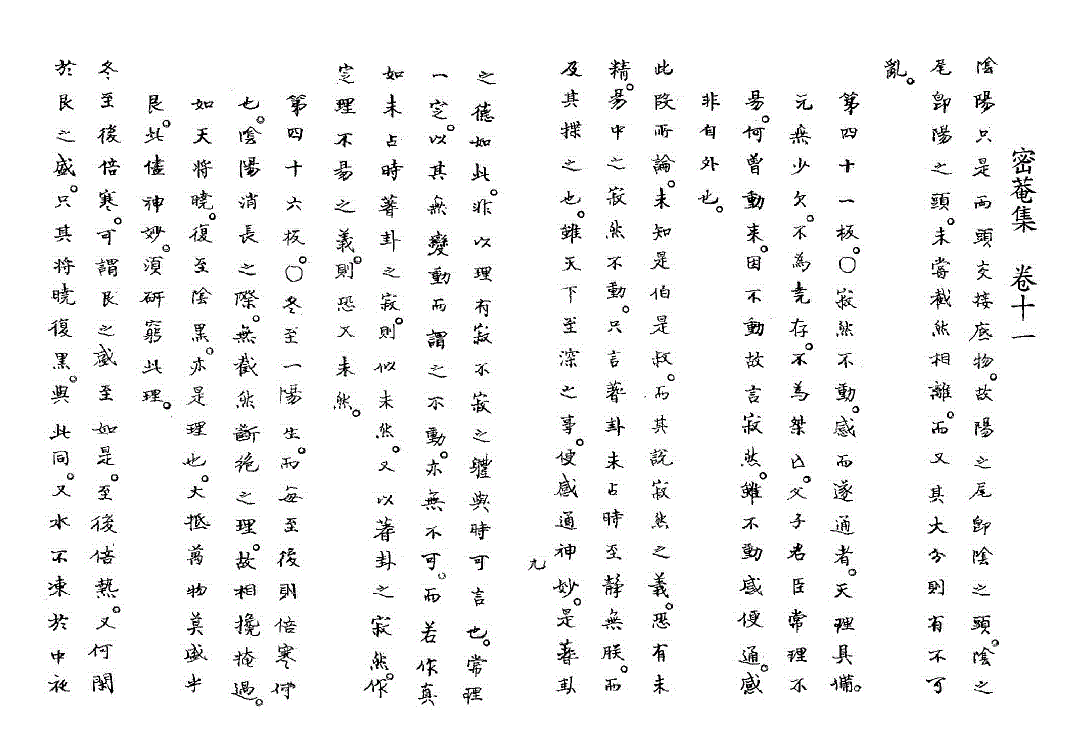 阴阳只是两头交接底物。故阳之尾即阴之头。阴之尾即阳之头。未尝截然相离。而又其大分则有不可乱。
阴阳只是两头交接底物。故阳之尾即阴之头。阴之尾即阳之头。未尝截然相离。而又其大分则有不可乱。第四十一板○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少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寂然。虽不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此段所论。未知是伯是叔。而其说寂然之义。恐有未精。易中之寂然不动。只言蓍卦未占时至静无朕。而及其揲之也。虽天下至深之事。便感通神妙。是蓍卦之德如此。非以理有寂不寂之体与时可言也。常理一定。以其无变动而谓之不动。亦无不可。而若作真如未占时蓍卦之寂。则似未然。又以蓍卦之寂然。作定理不易之义。则恐又未然。
第四十六板○冬至一阳生。而每至后则倍寒何也。阴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绝之理。故相搀掩过。如天将晓。复至阴黑。亦是理也。大抵万物莫盛乎艮。此尽神妙。须研穷此理。
冬至后倍寒。可谓艮之盛至如是。至后倍热。又何关于艮之盛。只其将晓复黑。与此同。又水不冻于中夜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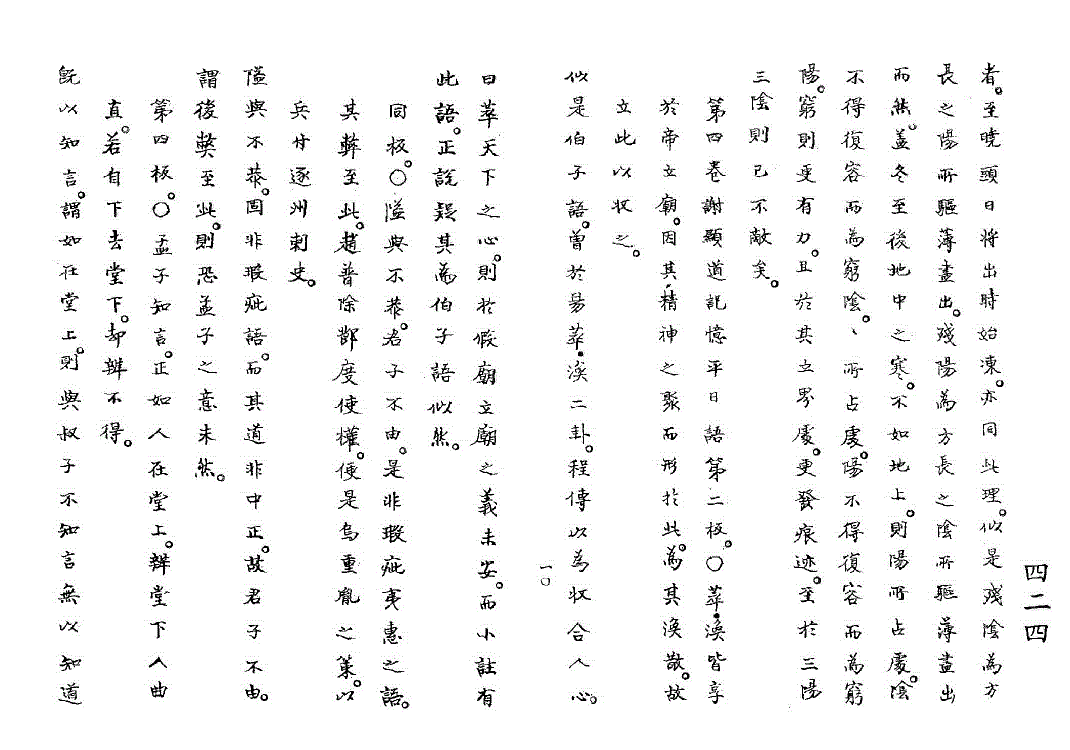 者。至晓头日将出时始冻。亦同此理。似是残阴为方长之阳所驱薄尽出。残阳为方长之阴所驱薄尽出而然。盖冬至后地中之寒。不如地上。则阳所占处。阴不得复容而为穷阴。阴所占处。阳不得复容而为穷阳。穷则更有力。且于其立界处。更发痕迹。至于三阳三阴则已不敌矣。
者。至晓头日将出时始冻。亦同此理。似是残阴为方长之阳所驱薄尽出。残阳为方长之阴所驱薄尽出而然。盖冬至后地中之寒。不如地上。则阳所占处。阴不得复容而为穷阴。阴所占处。阳不得复容而为穷阳。穷则更有力。且于其立界处。更发痕迹。至于三阳三阴则已不敌矣。第四卷谢显道记忆平日语第二板○萃,涣皆享于帝立庙。因其精神之聚而形于此。为其涣散。故立此以收之。
似是伯子语。曾于易萃,涣二卦。程传以为收合人心。曰萃天下之心。则于假庙立庙之义未安。而小注有此语。正说疑其为伯子语似然。
同板○隘与不恭。君子不由。是非瑕疵夷惠之语。其弊至此。赵普除节度使权。便是乌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
隘与不恭。固非瑕疵语。而其道非中正。故君子不由。谓后弊至此。则恐孟子之意未然。
第四板○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却辨不得。
既以知言。谓如在堂上。则与叔子不知言无以知道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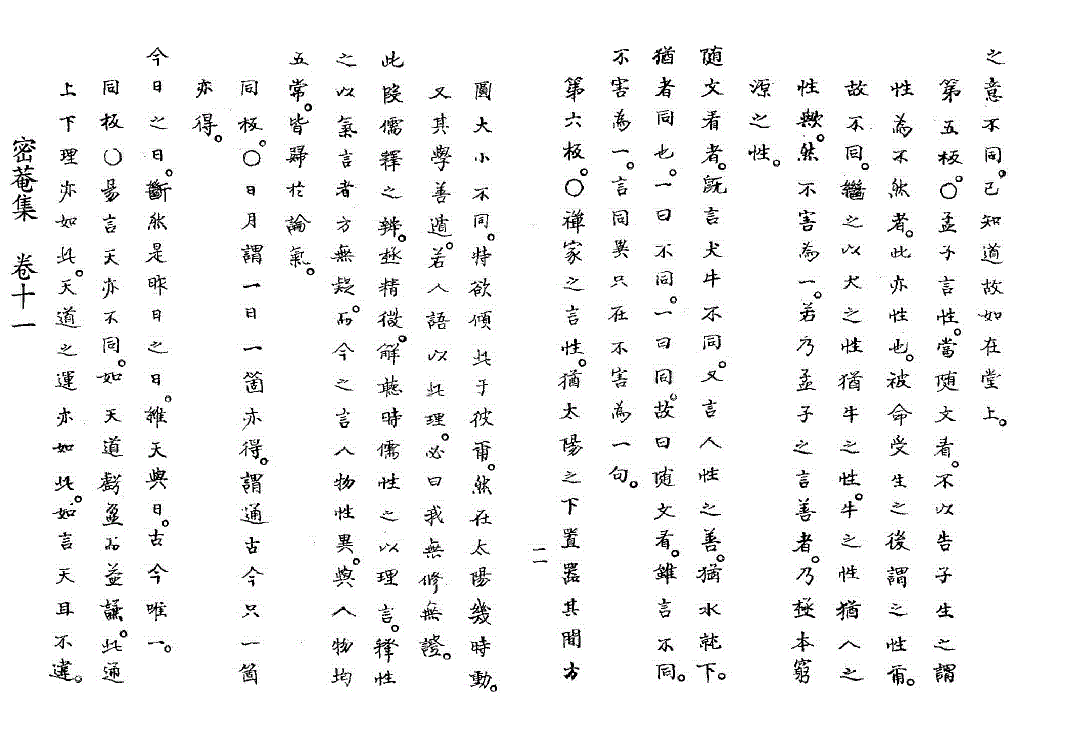 之意不同。已知道故如在堂上。
之意不同。已知道故如在堂上。第五板○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故不同。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
随文看者。既言犬牛不同。又言人性之善。犹水就下。犹者同也。一曰不同。一曰同。故曰随文看。虽言不同。不害为一。言同异只在不害为一句。
第六板○禅家之言性。犹太阳之下置器其间方圆大小不同。特欲倾此于彼尔。然在太阳几时动。又其学善遁。若人语以此理。必曰我无修无證。
此段儒释之辨。极精微。解听时儒性之以理言。释性之以气言者方无疑。而今之言人物性异。与人物均五常。皆归于论气。
同板○日月谓一日一个亦得。谓通古今只一个亦得。
今日之日。断然是昨日之日。维天与日。古今唯一。
同板○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亏盈而益谦。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运亦如此。如言天且不违。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5L 页
 况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直谓形而上者言。以鬼神为天地矣。
况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直谓形而上者言。以鬼神为天地矣。曰通上下。曰天道。曰形而上此三般分界。自程子已发。更无疑。但天且不违。非形而上。既谓是形而上。而又曰以鬼神为天地则未安。天且不违。鬼神只可兼形而上言。不得直以为形而上。
第十板○人之性。犹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动之物。
此须识得其意。若以不动字。真作性为静物则不可。不动亦不足以言性。性只此定理。定与静更别。
第五卷游定夫所录第六板○冯道更相数主。皆其雠也。安定以为当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雠无伤也。荀彧佐曹操诛伐。而卒死于操。君实以为东汉之衰。彧与攸视天下。无足与安刘氏者。惟操为可依。故俯首从之。方是时。未知操有他志。君子曰在道为不忠。在彧为不知。如以为事固有轻重之权。方以天下为心。未暇恤人议己也。则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胡公温公之论。虽是论一事之差。身当其地。则将自为其人者也。所关不小。人之难信有如此。可不惧。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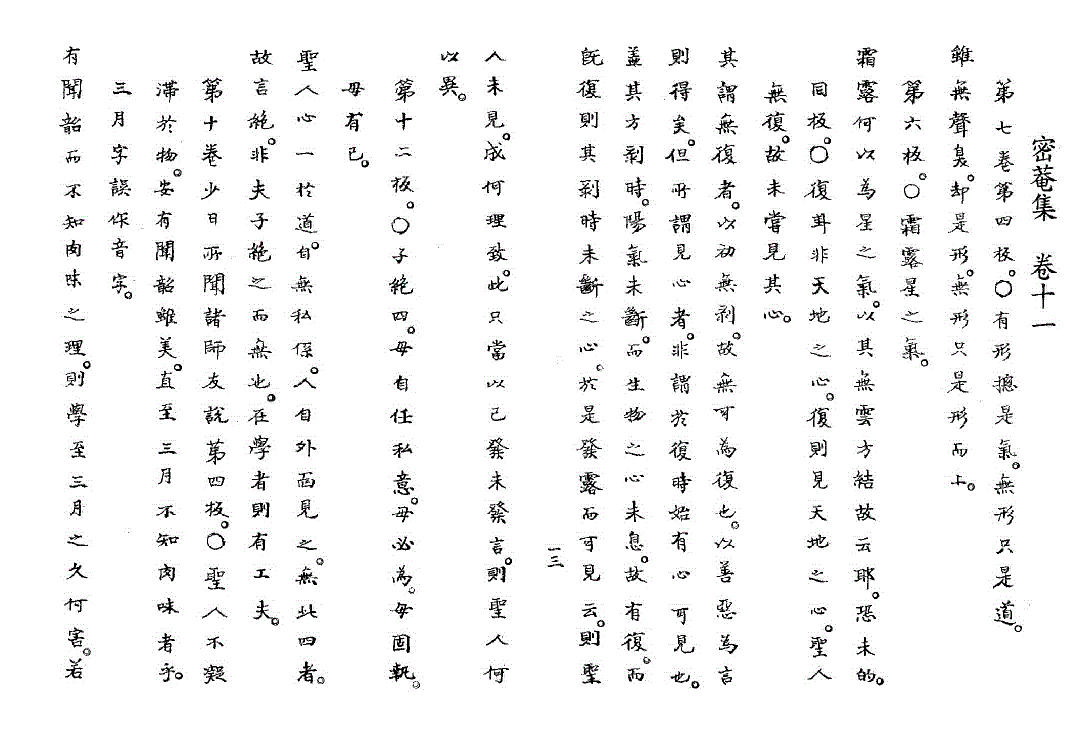 第七卷第四板○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
第七卷第四板○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虽无声臭。却是形。无形只是形而上。
第六板○霜露星之气。
霜露何以为星之气。以其无云方结故云耶。恐未的。
同板○复卦非天地之心。复则见天地之心。圣人无复。故未尝见其心。
其谓无复者。以初无剥。故无可为复也。以善恶为言则得矣。但所谓见心者。非谓于复时始有心可见也。盖其方剥时。阳气未断。而生物之心未息。故有复。而既复则其剥时未断之心。于是发露而可见云。则圣人未见。成何理致。此只当以已发未发言。则圣人何以异。
第十二板○子绝四。毋自任私意。毋必为。毋固执。毋有己。
圣人心一于道。自无私系。人自外面见之。无此四者。故言绝。非夫子绝之而无也。在学者则有工夫。
第十卷少日所闻诸师友说第四板○圣人不凝滞于物。安有闻韶虽美。直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误依音字。
有闻韶而不知肉味之理。则学至三月之久何害。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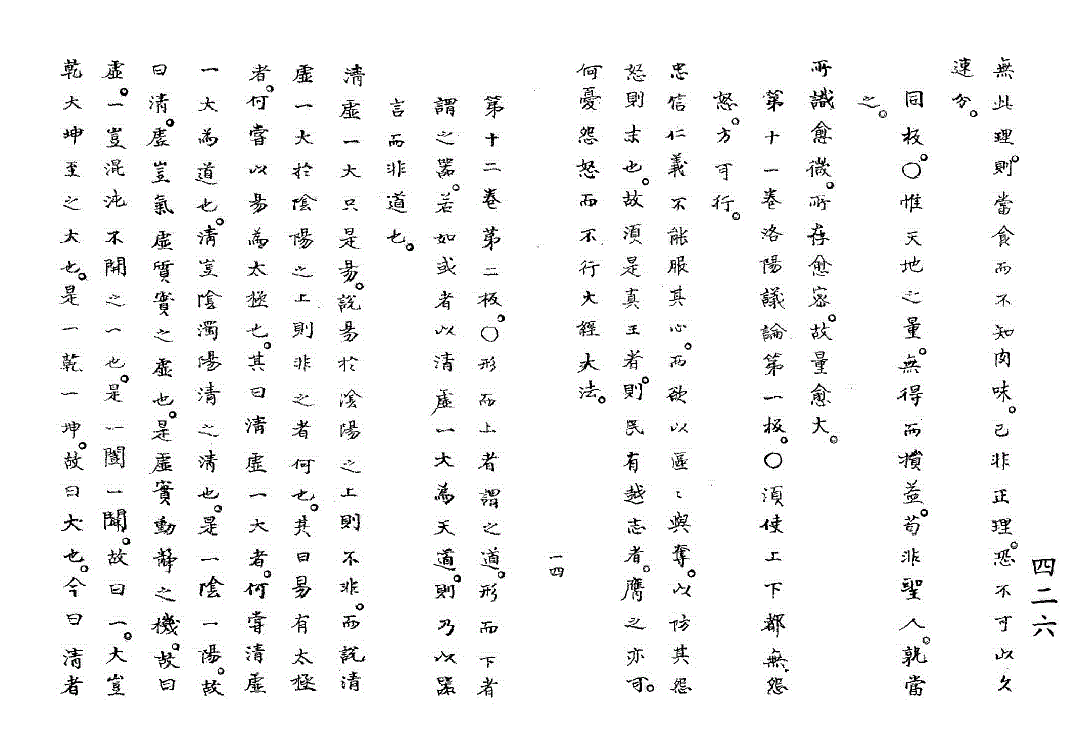 无此理。则当食而不知肉味。已非正理。恐不可以久速分。
无此理。则当食而不知肉味。已非正理。恐不可以久速分。同板○惟天地之量。无得而损益。苟非圣人。孰当之。
所识愈微。所存愈密。故量愈大。
第十一卷洛阳议论第一板○须使上下都无怨怒。方可行。
忠信仁义不能服其心。而欲以区区与夺。以防其怨怒则末也。故须是真王者。则民有越志者。膺之亦可。何忧怨怒而不行大经大法。
第十二卷第二板○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清虚一大只是易。说易于阴阳之上则不非。而说清虚一大于阴阳之上则非之者何也。其曰易有太极者。何尝以易为太极也。其曰清虚一大者。何尝清虚一大为道也。清岂阴浊阳清之清也。是一阴一阳。故曰清。虚岂气虚质实之虚也。是虚实动静之机。故曰虚。一岂混沌不开之一也。是一阖一辟。故曰一。大岂乾大坤至之大也。是一乾一坤。故曰大也。今曰清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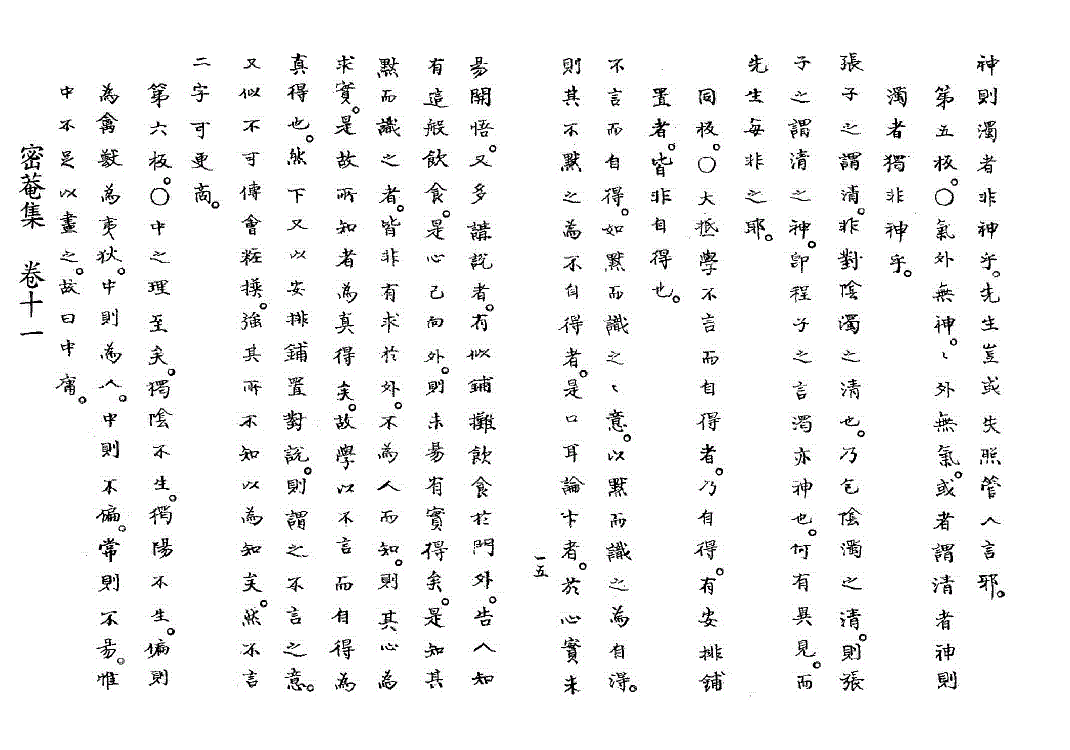 神则浊者非神乎。先生岂或失照管人言邪。
神则浊者非神乎。先生岂或失照管人言邪。第五板○气外无神。神外无气。或者谓清者神则浊者独非神乎。
张子之谓清。非对阴浊之清也。乃包阴浊之清。则张子之谓清之神。即程子之言浊亦神也。何有异见。而先生每非之耶。
同板○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有安排铺置者。皆非自得也。
不言而自得。如默而识之之意。以默而识之为自得。则其不默之为不自得者。是口耳论卞者。于心实未易开悟。又多讲说者。有似铺摊饮食于门外。告人知有这般饮食。是心已向外。则未易有实得矣。是知其默而识之者。皆非有求于外。不为人而知。则其心为求实。是故所知者为真得矣。故学以不言而自得为真得也。然下又以安排铺置对说。则谓之不言之意。又似不可傅会妆撰。强其所不知以为知矣。然不言二字可更商。
第六板○中之理至矣。独阴不生。独阳不生。偏则为禽兽为夷狄。中则为人。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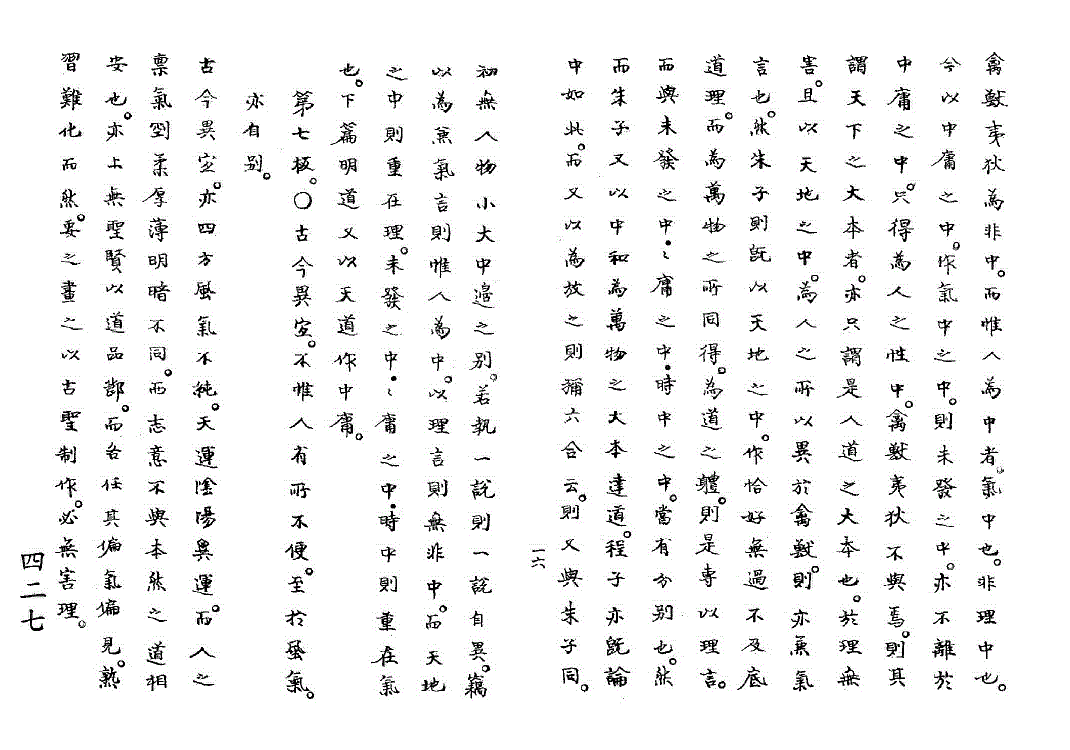 禽兽夷狄为非中。而惟人为中者。气中也。非理中也。今以中庸之中。作气中之中。则未发之中。亦不离于中庸之中。只得为人之性中。禽兽夷狄不与焉。则其谓天下之大本者。亦只谓是人道之大本也。于理无害。且以天地之中。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则亦兼气言也。然朱子则既以天地之中。作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而为万物之所同得。为道之体。则是专以理言。而与未发之中,中庸之中,时中之中。当有分别也。然而朱子又以中和为万物之大本达道。程子亦既论中如此。而又以为放之则弥六合云。则又与朱子同。初无人物小大中边之别。若执一说则一说自异。窃以为兼气言则惟人为中。以理言则无非中。而天地之中则重在理。未发之中,中庸之中,时中则重在气也。下篇明道又以天道作中庸。
禽兽夷狄为非中。而惟人为中者。气中也。非理中也。今以中庸之中。作气中之中。则未发之中。亦不离于中庸之中。只得为人之性中。禽兽夷狄不与焉。则其谓天下之大本者。亦只谓是人道之大本也。于理无害。且以天地之中。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则亦兼气言也。然朱子则既以天地之中。作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而为万物之所同得。为道之体。则是专以理言。而与未发之中,中庸之中,时中之中。当有分别也。然而朱子又以中和为万物之大本达道。程子亦既论中如此。而又以为放之则弥六合云。则又与朱子同。初无人物小大中边之别。若执一说则一说自异。窃以为兼气言则惟人为中。以理言则无非中。而天地之中则重在理。未发之中,中庸之中,时中则重在气也。下篇明道又以天道作中庸。第七板○古今异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风气。亦自别。
古今异宜。亦四方风气不纯。天运阴阳异运。而人之禀气刚柔厚薄明暗不同。而志意不与本然之道相安也。亦上无圣贤以道品节。而各任其偏气偏见。熟习难化而然。要之画之以古圣制作。必无害理。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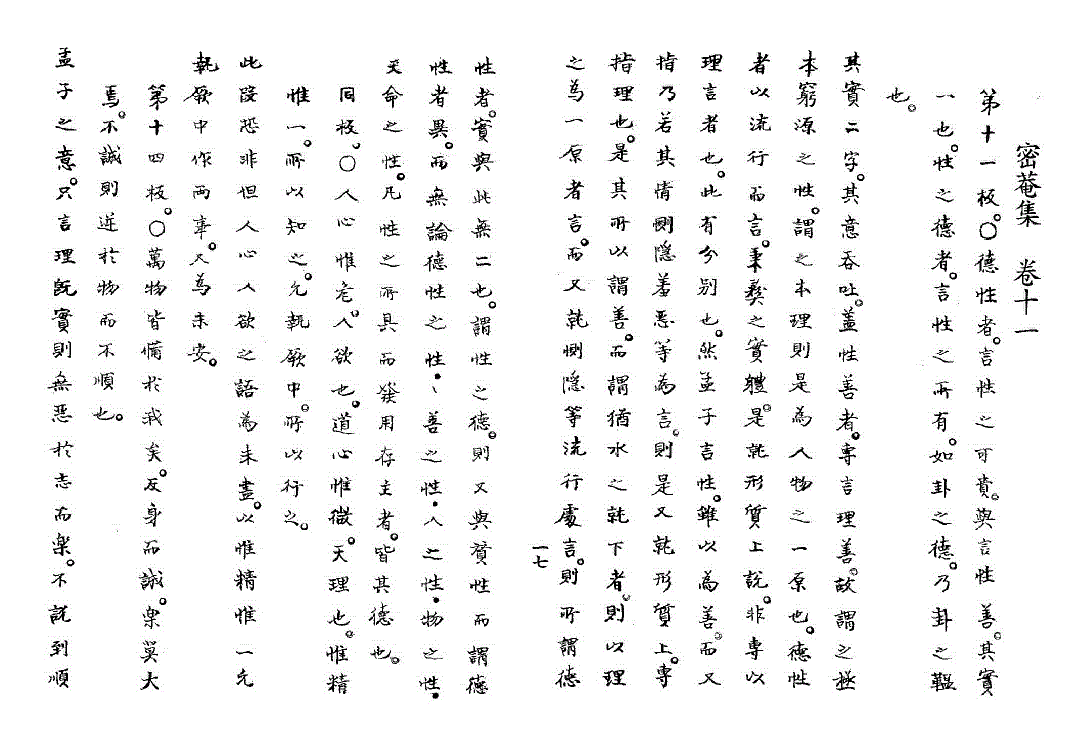 第十一板○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鞰也。
第十一板○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鞰也。其实二字。其意吞吐。盖性善者。专言理善。故谓之极本穷源之性。谓之本理则是为人物之一原也。德性者以流行而言。秉彝之实体。是就形质上说。非专以理言者也。此有分别也。然孟子言性。虽以为善。而又指乃若其情恻隐羞恶等为言。则是又就形质上。专指理也。是其所以谓善。而谓犹水之就下者。则以理之为一原者言。而又就恻隐等流行处言。则所谓德性者。实与此无二也。谓性之德。则又与赞性而谓德性者异。而无论德性之性,性善之性,人之性,物之性,天命之性。凡性之所具而发用存主者。皆其德也。
同板○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知之。允执厥中。所以行之。
此段恐非但人心人欲之语为未尽。以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两事。又为未安。
第十四板○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诚则逆于物而不顺也。
孟子之意。只言理既实则无恶于志而乐。不说到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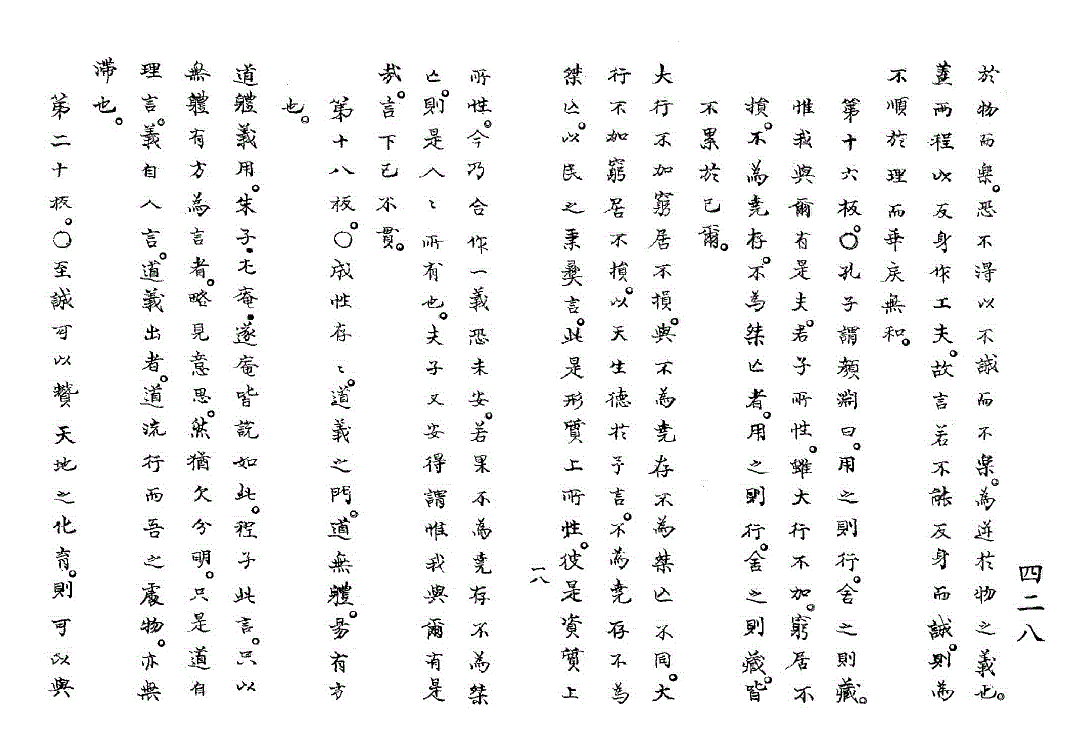 于物而乐。恐不得以不诚而不乐。为逆于物之义也。盖两程以反身作工夫。故言若不能反身而诚。则为不顺于理而乖戾无和。
于物而乐。恐不得以不诚而不乐。为逆于物之义也。盖两程以反身作工夫。故言若不能反身而诚。则为不顺于理而乖戾无和。第十六板○孔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皆不累于己尔。
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与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同。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以天生德于予言。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以民之秉彝言。此是形质上所性。彼是资质上所性。今乃合作一义恐未安。若果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则是人人所有也。夫子又安得谓惟我与尔有是哉。言下已不贯。
第十八板○成性存存。道义之门。道无体。易有方也。
道体义用。朱子,尤庵,遂庵皆说如此。程子此言。只以无体有方为言者。略见意思。然犹欠分明。只是道自理言。义自人言。道义出者。道流行而吾之处物。亦无滞也。
第二十板○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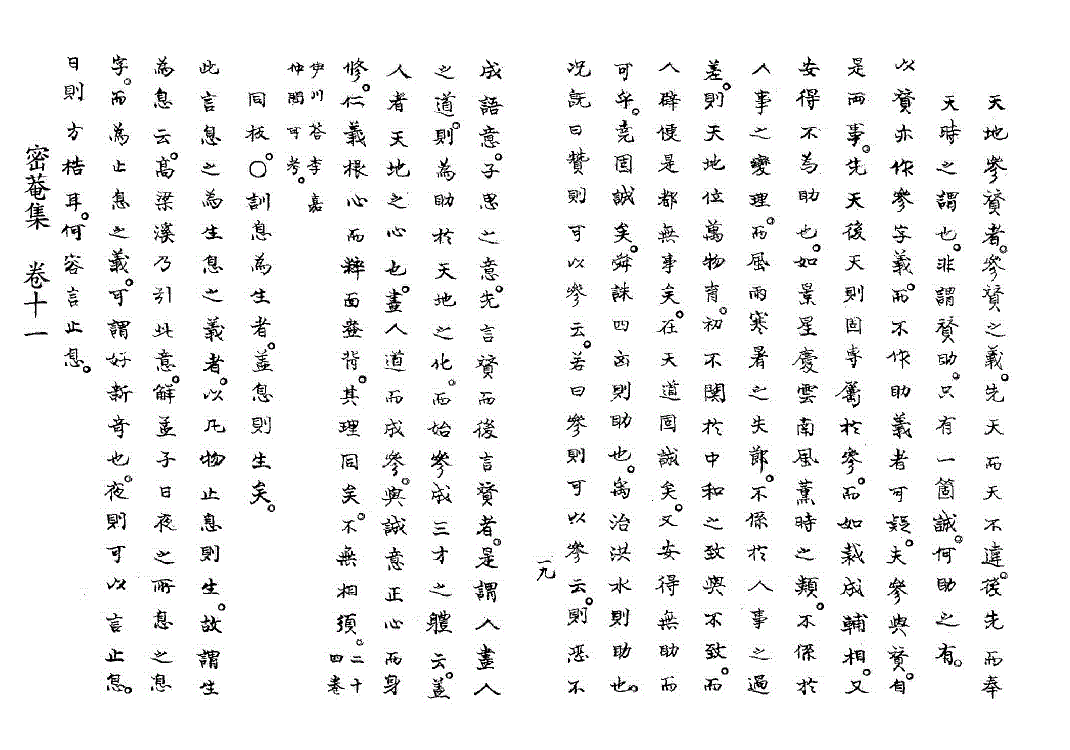 天地参赞者。参赞之义。先天而天不违。后先而奉天时之谓也。非谓赞助。只有一个诚。何助之有。
天地参赞者。参赞之义。先天而天不违。后先而奉天时之谓也。非谓赞助。只有一个诚。何助之有。以赞亦作参字义。而不作助义者可疑。夫参与赞。自是两事。先天后天则固专属于参。而如裁成辅相。又安得不为助也。如景星庆云南风薰时之类。不系于人事之变理。而风雨寒暑之失节。不系于人事之过差。则天地位万物育。初不关于中和之致与不致。而人辟便是都无事矣。在天道固诚矣。又安得无助而可乎。尧固诚矣。舜诛四凶则助也。禹治洪水则助也。况既曰赞则可以参云。若曰参则可以参云。则恐不成语意。子思之意。先言赞而后言赞者。是谓人尽人之道。则为助于天地之化。而始参成三才之体云。盖人者天地之心也。尽人道而成参。与诚意正心而身修。仁义根心而粹面盎背。其理同矣。不无相须。(二十四卷伊川答李嘉仲问可考。)
同板○训息为生者。盖息则生矣。
此言息之为生息之义者。以凡物止息则生。故谓生为息云。高梁溪乃引此意。解孟子日夜之所息之息字。而为止息之义。可谓好新奇也。夜则可以言止息。日则方梏耳。何容言止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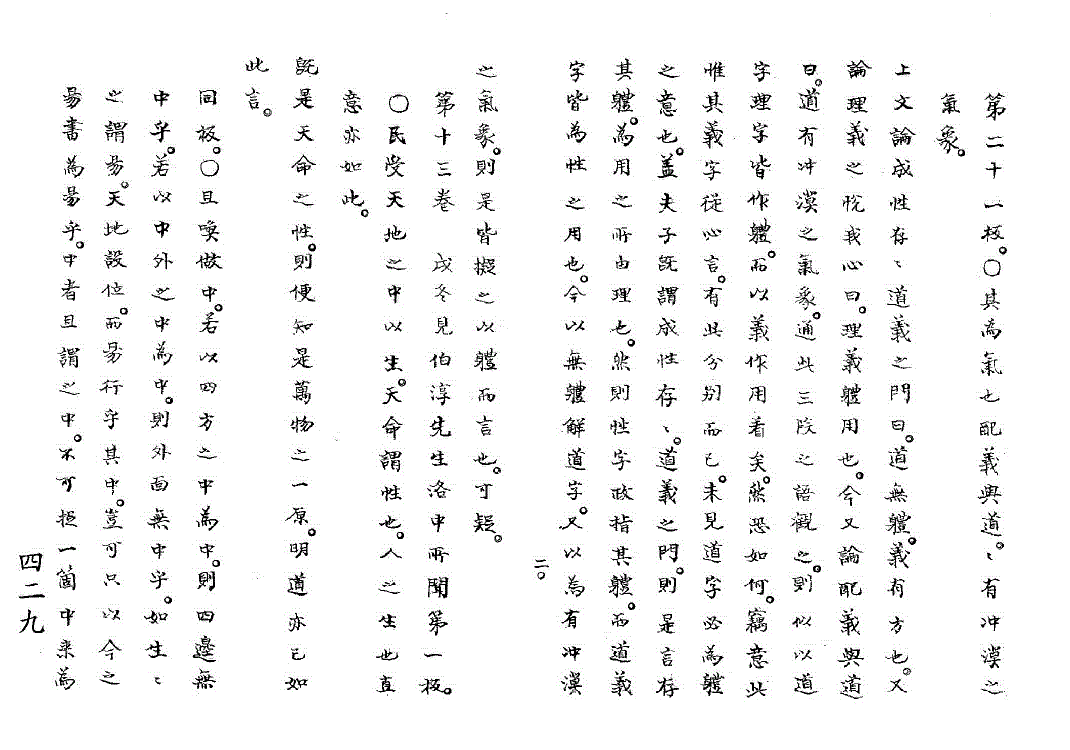 第二十一板○其为气也配义与道。道有冲漠之气象。
第二十一板○其为气也配义与道。道有冲漠之气象。上文论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曰。道无体。义有方也。又论理义之悦我心曰。理义体用也。今又论配义与道曰。道有冲漠之气象。通此三段之语观之。则似以道字理字皆作体。而以义作用看矣。然恐如何。窃意此惟其义字从心言。有此分别而已。未见道字必为体之意也。盖夫子既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则是言存其体。为用之所由理也。然则性字政指其体。而道义字皆为性之用也。今以无体解道字。又以为有冲漠之气象。则是皆拟之以体而言也。可疑。
第十三卷▣戌冬见伯淳先生洛中所闻第一板○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谓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既是天命之性。则便知是万物之一原。明道亦已如此言。
同板○且唤做中。若以四方之中为中。则四边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为中。则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岂可只以今之易书为易乎。中者且谓之中。不可捉一个中来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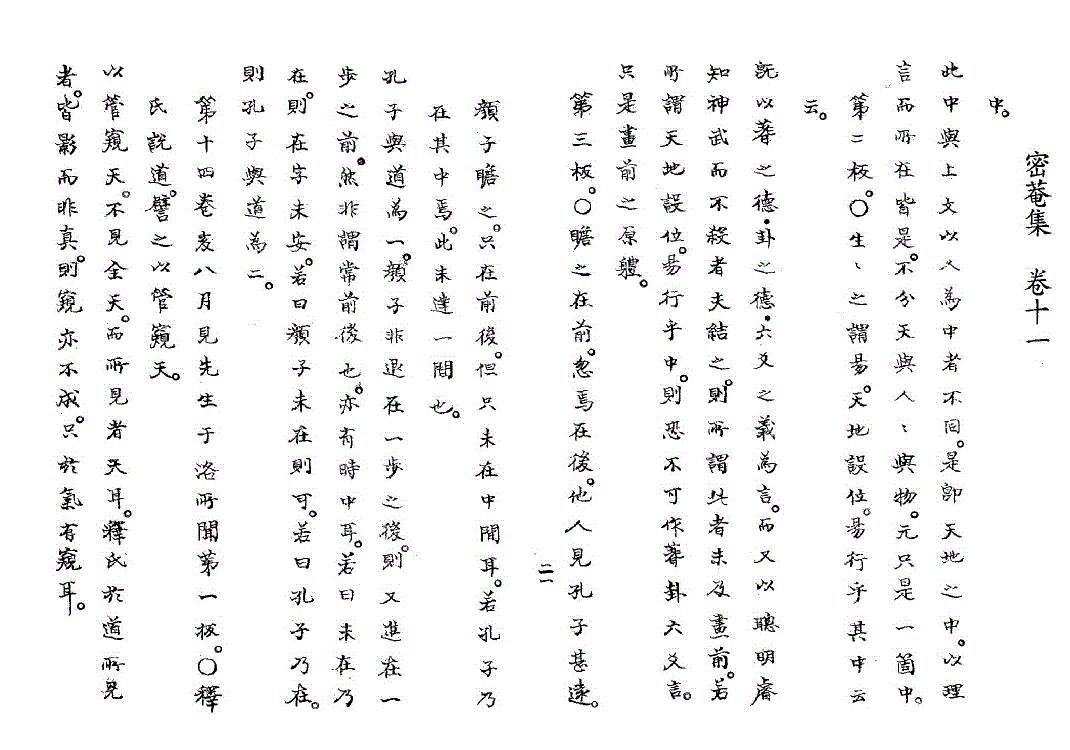 中。
中。此中与上文以人为中者不同。是即天地之中。以理言而所在皆是。不分天与人人与物。元只是一个中。
第二板○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易行乎其中云云。
既以蓍之德,卦之德,六爻之义为言。而又以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结之。则所谓此者未及画前。若所谓天地设位。易行乎中。则恐不可作蓍卦六爻言。只是画前之原体。
第三板○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他人见孔子甚远。颜子瞻之。只在前后。但只未在中间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达一间也。
孔子与道为一。颜子非退在一步之后。则又进在一步之前。然非谓常前后也。亦有时中耳。若曰未在乃在。则在字未安。若曰颜子未在则可。若曰孔子乃在。则孔子与道为二。
第十四卷亥八月见先生于洛所闻第一板○释氏说道。譬之以管窥天。
以管窥天。不见全天。而所见者天耳。释氏于道所见者。皆影而非真。则窥亦不成。只于气有窥耳。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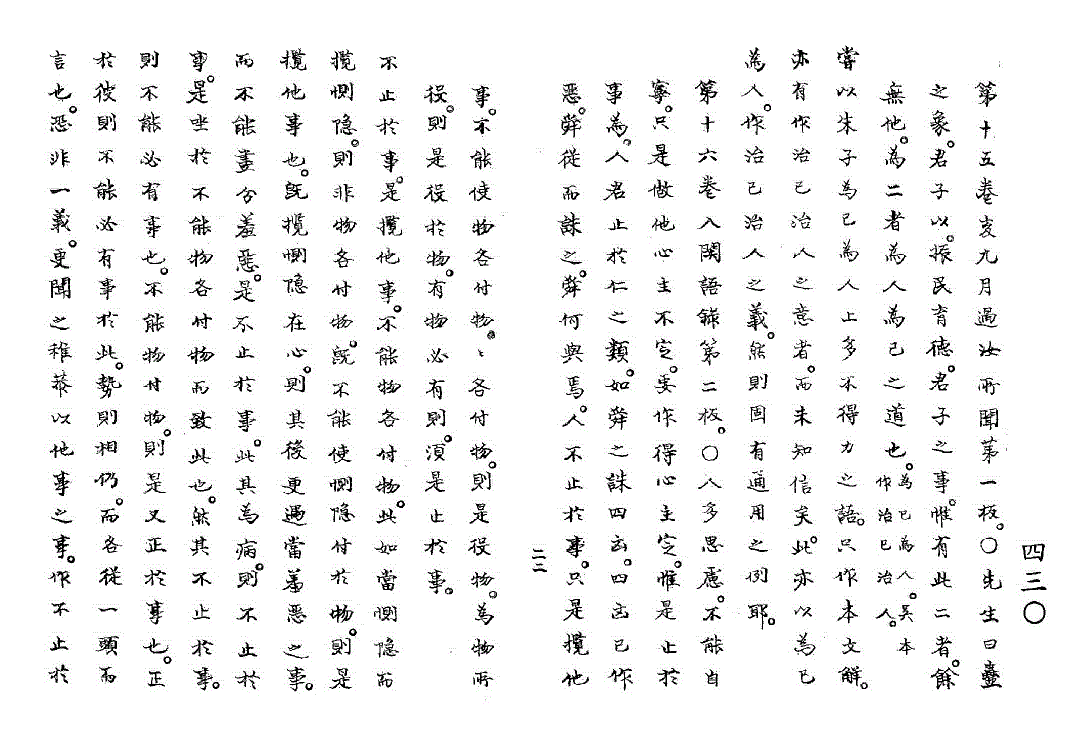 第十五卷亥九月过汝所闻第一板○先生曰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馀无他。为二者为人为己之道也。(为己为人。吴本作治己治人。)
第十五卷亥九月过汝所闻第一板○先生曰蛊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馀无他。为二者为人为己之道也。(为己为人。吴本作治己治人。)尝以朱子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之语。只作本文解。亦有作治己治人之意者。而未知信矣。此亦以为己为人。作治己治人之义。然则固有通用之例耶。
第十六卷入关语录第二板○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之类。如舜之诛四凶。四凶已作恶。舜从而诛之。舜何与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
不止于事。是揽他事。不能物各付物。此如当恻隐而揽恻隐。则非物各付物。既不能使恻隐付于物。则是揽他事也。既揽恻隐在心。则其后更遇当羞恶之事。而不能尽分羞恶。是不止于事。此其为病。则不止于事。是坐于不能物各付物而致此也。然其不止于事。则不能必有事也。不能物付物。则是又正于事也。正于彼则不能必有事于此。势则相仍。而各从一头而言也。恐非一义。更闻之稚恭以他事之事。作不止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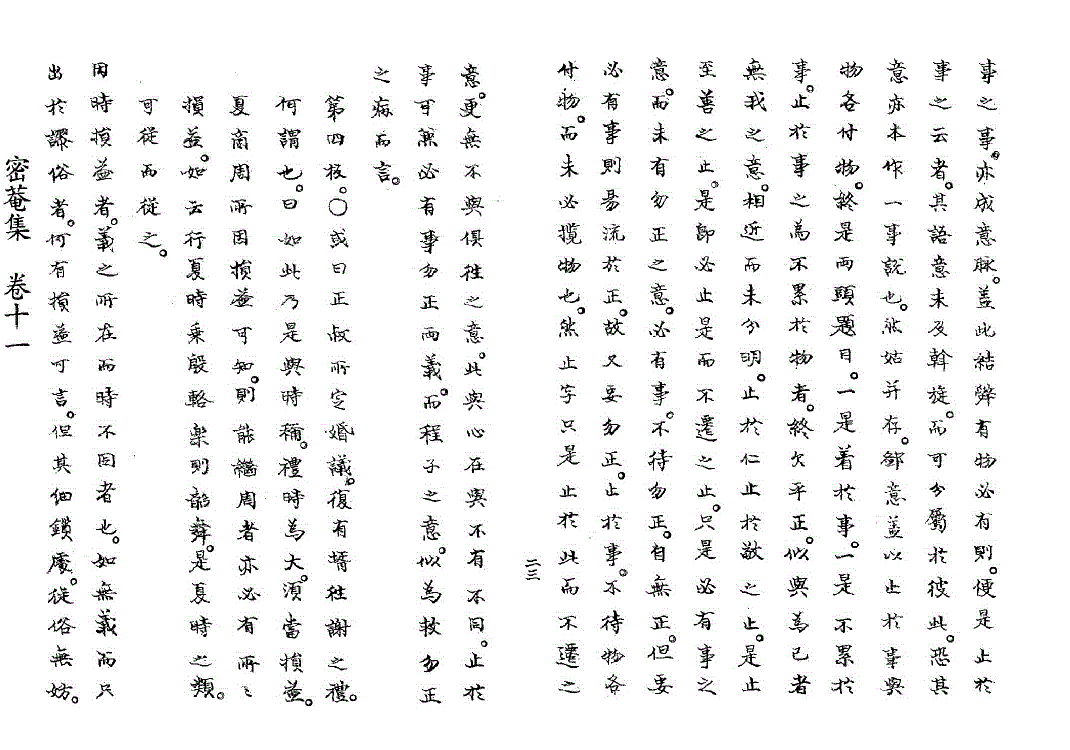 事之事。亦成意脉。盖此结辞有物必有则。便是止于事之云者。其语意未及斡旋。而可分属于彼此。恐其意亦本作一事说也。然姑并存。鄙意盖以止于事与物各付物。终是两头题目。一是着于事。一是不累于事。止于事之为不累于物者。终欠平正。似与为己者无我之意。相近而未分明。止于仁止于敬之止。是止至善之止。是即必止是而不迁之止。只是必有事之意。而未有勿正之意。必有事。不待勿正。自无正。但要必有事则易流于正。故又要勿正。止于事。不待物各付物。而未必揽物也。然止字只是止于此而不迁之意。更无不与俱往之意。此与心在与不有不同。止于事可兼必有事勿正两义。而程子之意。似为救勿正之病而言。
事之事。亦成意脉。盖此结辞有物必有则。便是止于事之云者。其语意未及斡旋。而可分属于彼此。恐其意亦本作一事说也。然姑并存。鄙意盖以止于事与物各付物。终是两头题目。一是着于事。一是不累于事。止于事之为不累于物者。终欠平正。似与为己者无我之意。相近而未分明。止于仁止于敬之止。是止至善之止。是即必止是而不迁之止。只是必有事之意。而未有勿正之意。必有事。不待勿正。自无正。但要必有事则易流于正。故又要勿正。止于事。不待物各付物。而未必揽物也。然止字只是止于此而不迁之意。更无不与俱往之意。此与心在与不有不同。止于事可兼必有事勿正两义。而程子之意。似为救勿正之病而言。第四板○或曰正叔所定婚议。复有婿往谢之礼。何谓也。曰如此乃是与时称。礼时为大。须当损益。夏商周所因损益可知。则能继周者亦必有所所损益。如云行夏时乘殷辂乐则韶舞。是夏时之类。可从而从之。
因时损益者。义之所在而时不同者也。如无义而只出于谬俗者。何有损益可言。但其细锁处。从俗无妨。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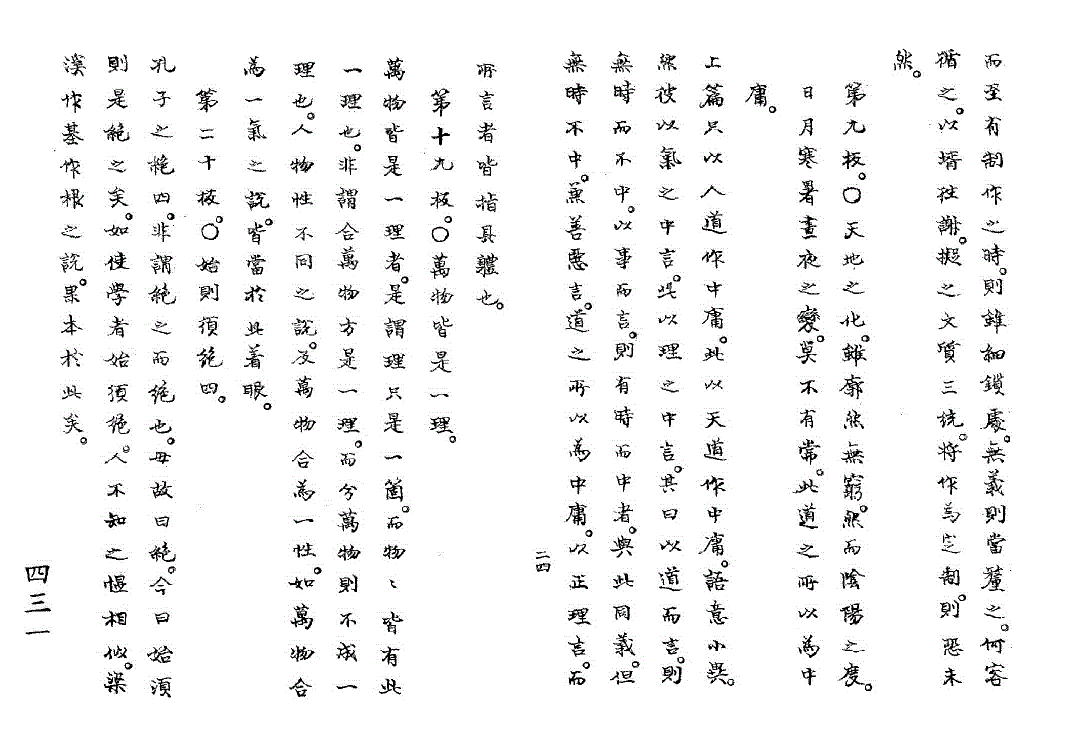 而至有制作之时。则虽细锁处。无义则当釐之。何容循之。以婿往谢。拟之文质三统。将作为定制。则恐未然。
而至有制作之时。则虽细锁处。无义则当釐之。何容循之。以婿往谢。拟之文质三统。将作为定制。则恐未然。第九板○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
上篇只以人道作中庸。此以天道作中庸。语意小异。然彼以气之中言。此以理之中言。其曰以道而言。则无时而不中。以事而言。则有时而中者。与此同义。但无时不中。兼善恶言。道之所以为中庸。以正理言。而所言者皆指具体也。
第十九板○万物皆是一理。
万物皆是一理者。是谓理只是一个。而物物皆有此一理也。非谓合万物方是一理。而分万物则不成一理也。人物性不同之说。及万物合为一性。如万物合为一气之说。皆当于此着眼。
第二十板○始则须绝四。
孔子之绝四。非谓绝之而绝也。毋故曰绝。今曰始须则是绝之矣。如使学者始须绝。人不知之愠相似。梁溪作基作根之说。果本于此矣。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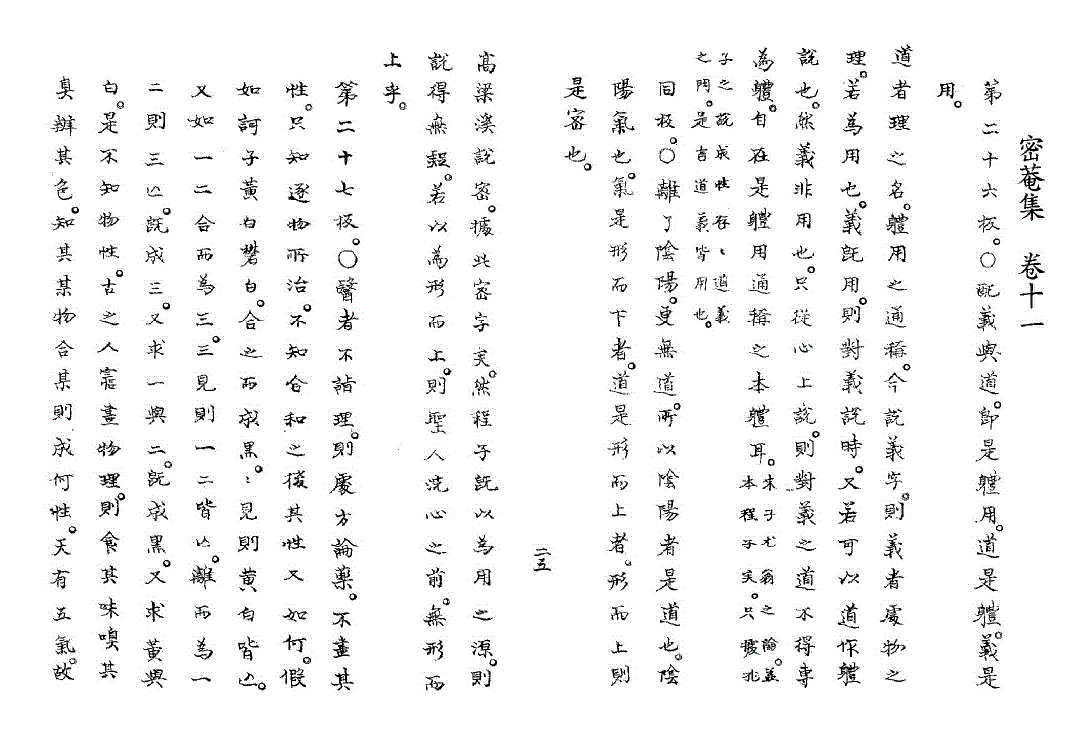 第二十六板○配义与道。即是体用。道是体。义是用。
第二十六板○配义与道。即是体用。道是体。义是用。道者理之名。体用之通称。今说义字。则义者处物之理。若为用也。义既用。则对义说时。又若可以道作体说也。然义非用也。只从心上说。则对义之道不得专为体。自在是体用通称之本体耳。(朱子尤翁之论。盖本程子矣。只据孔子之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言道义皆用也。)
同板○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则是密也。
高梁溪说密。据此密字矣。然程子既以为用之源。则说得无疑。若以为形而上。则圣人洗心之前。无形而上乎。
第二十七板○医者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后其性又如何。假如诃子黄白矾白。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则一二皆亡。离而为一二则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天有五气。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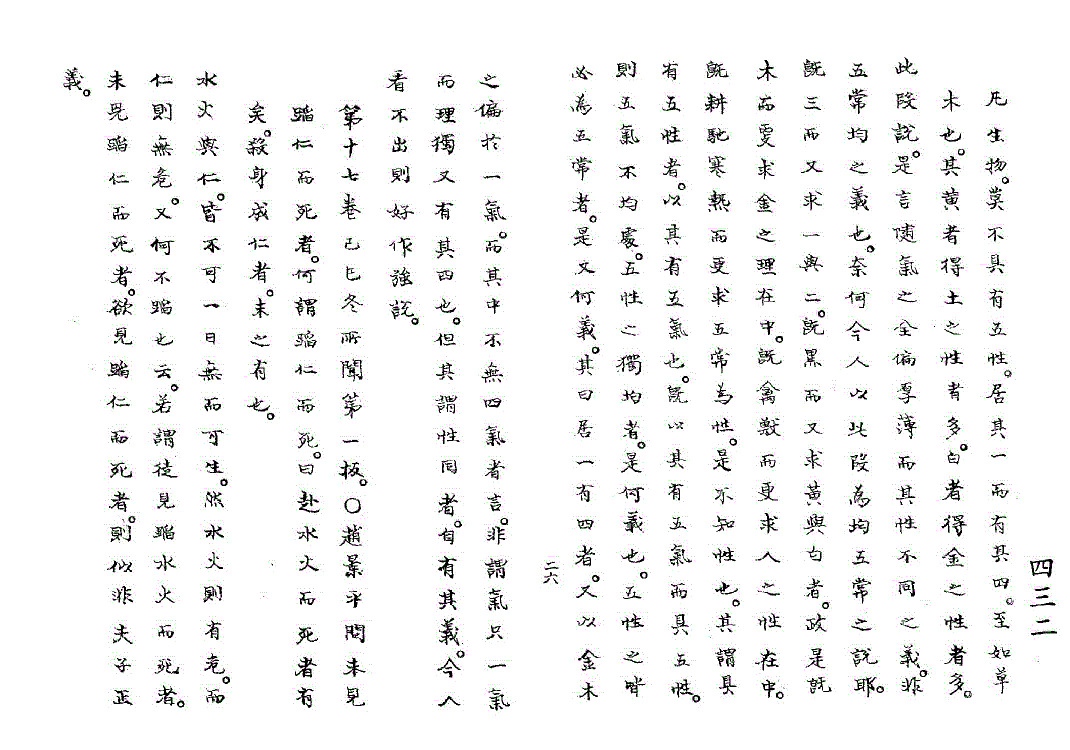 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者多。白者得金之性者多。
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者多。白者得金之性者多。此段说。是言随气之全偏厚薄而其性不同之义。非五常均之义也。奈何今人以此段为均五常之说耶。既三而又求一与二。既黑而又求黄与白者。政是既木而更求金之理在中。既禽兽而更求人之性在中。既耕驰寒热而更求五常为性。是不知性也。其谓具有五性者。以其有五气也。既以其有五气而具五性。则五气不均处。五性之独均者。是何义也。五性之皆必为五常者。是又何义。其曰居一有四者。又以金木之偏于一气。而其中不无四气者言。非谓气只一气而理独又有其四也。但其谓性同者。自有其义。今人看不出则好作强说。
第十七卷己巳冬所闻第一板○赵景平问未见蹈仁而死者。何谓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杀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水火与仁。皆不可一日无而可生。然水火则有危。而仁则无危。又何不蹈也云。若谓徒见蹈水火而死者。未见蹈仁而死者。欲见蹈仁而死者。则似非夫子正义。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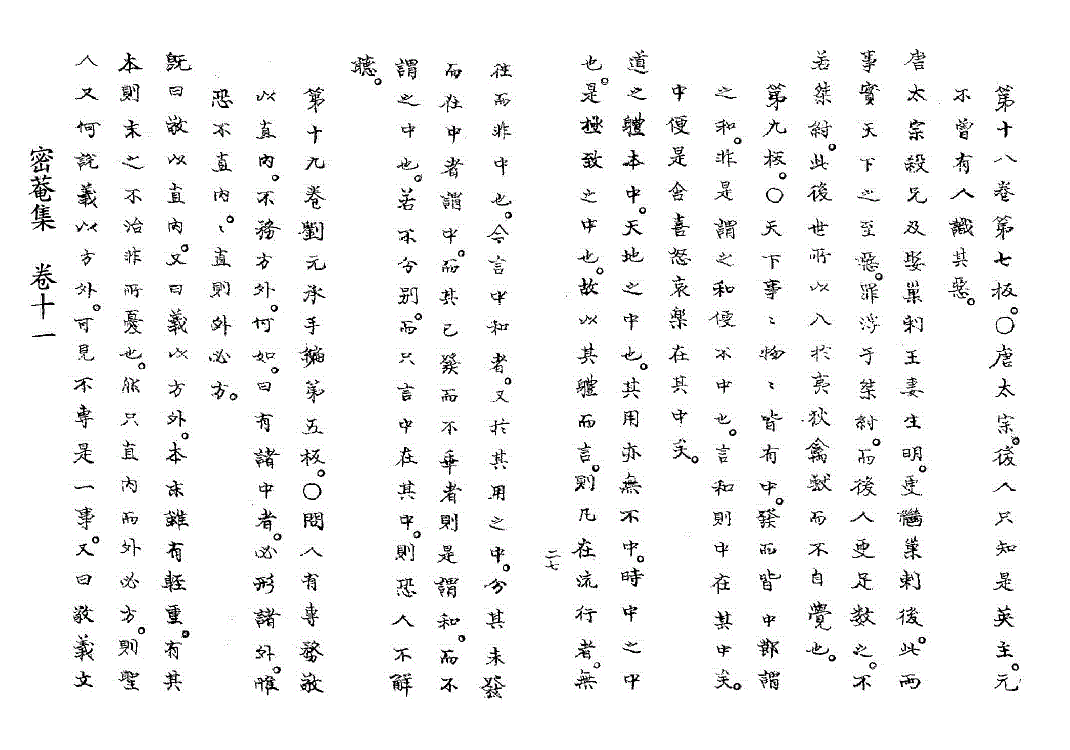 第十八卷第七板○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
第十八卷第七板○唐太宗。后人只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识其恶。唐太宗杀兄及娶巢剌王妻生明。更继巢剌后。此两事实天下之至恶。罪浮于桀纣。而后人更足数之。不若桀纣。此后世所以入于夷狄禽兽而不自觉也。
第九板○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非是谓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则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乐在其中矣。
道之体本中。天地之中也。其用亦无不中。时中之中也。是极致之中也。故以其体而言。则凡在流行者。无往而非中也。今言中和者。又于其用之中。分其未发而在中者谓中。而其已发而不乖者则是谓和。而不谓之中也。若不分别。而只言中在其中。则恐人不解听。
第十九卷刘元承手编第五板○问人有专务敬以直内。不务方外。何如。曰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惟恐不直内。内直则外必方。
既曰敬以直内。又曰义以方外。本末虽有轻重。有其本则末之不治非所忧也。然只直内而外必方。则圣人又何说义以方外。可见不专是一事。又曰敬义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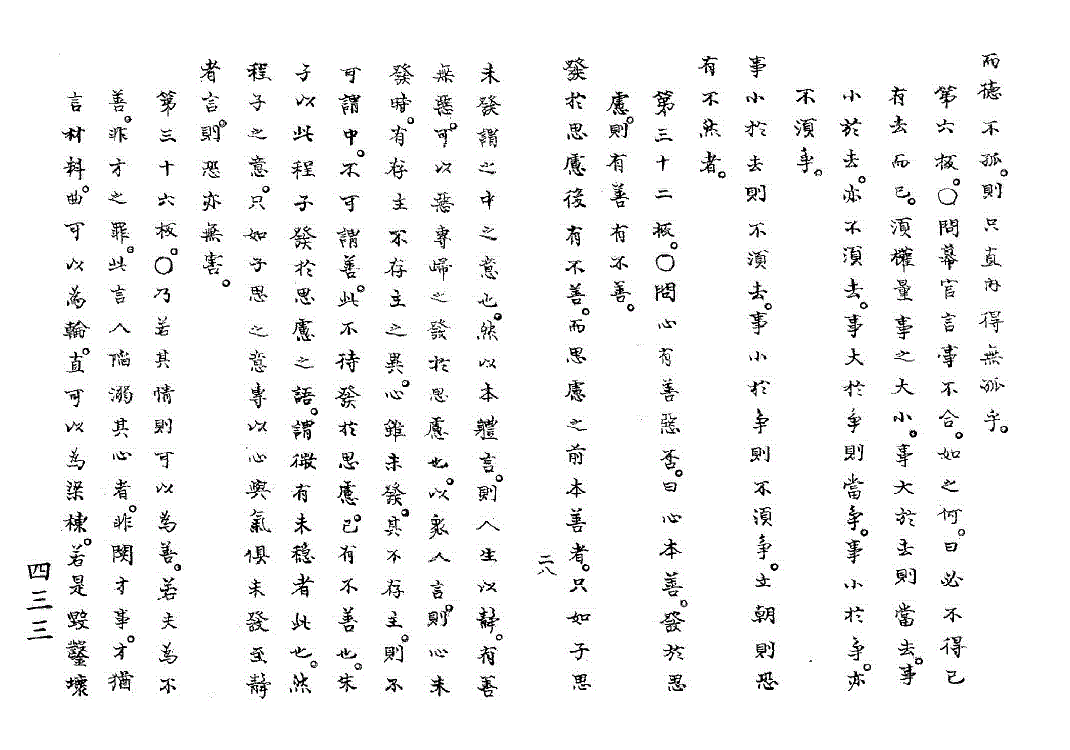 而德不孤。则只直内得无孤乎。
而德不孤。则只直内得无孤乎。第六板○问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须权量事之大小。事大于去则当去。事小于去。亦不须去。事大于争则当争。事小于争。亦不须争。
事小于去则不须去。事小于争则不须争。立朝则恐有不然者。
第三十二板○问心有善恶否。曰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
发于思虑后有不善。而思虑之前本善者。只如子思未发谓之中之意也。然以本体言。则人生以静。有善无恶。可以恶专归之发于思虑也。以众人言。则心未发时。有存主不存主之异。心虽未发。其不存主。则不可谓中。不可谓善。此不待发于思虑。已有不善也。朱子以此程子发于思虑之语。谓微有未稳者此也。然程子之意。只如子思之意专以心与气俱未发至静者言。则恐亦无害。
第三十六板○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关才事。才犹言材料。曲可以为轮。直可以为梁栋。若是毁凿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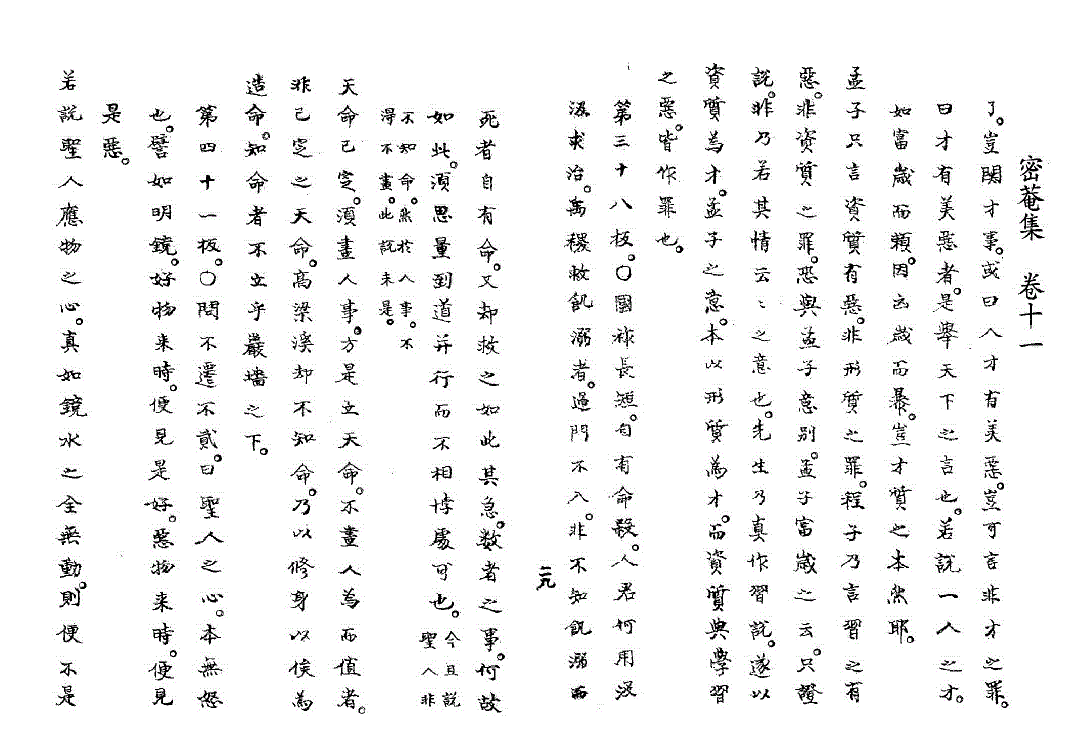 了。岂关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恶。岂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恶者。是举天下之言也。若说一人之才。如富岁而赖。因凶岁而暴。岂才质之本然耶。
了。岂关才事。或曰人才有美恶。岂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恶者。是举天下之言也。若说一人之才。如富岁而赖。因凶岁而暴。岂才质之本然耶。孟子只言资质有恶。非形质之罪。程子乃言习之有恶。非资质之罪。恐与孟子意别。孟子富岁之云。只證说。非乃若其情云云之意也。先生乃真作习说。遂以资质为才。孟子之意。本以形质为才。而资质典学习之恶。皆作罪也。
第三十八板○国祚长短。自有命杀。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饥溺者。过门不入。非不知饥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数者之事。何故如此。须思量到道并行而不相悖处可也。(今且说圣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尽。此说未是。)
天命已定。须尽人事。方是立天命。不尽人为而值者。非已定之天命。高梁溪却不知命。乃以修身以俟为造命。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第四十一板○问不迁不贰。曰圣人之心。本无怒也。譬如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
若说圣人应物之心。真如镜水之全无动。则便不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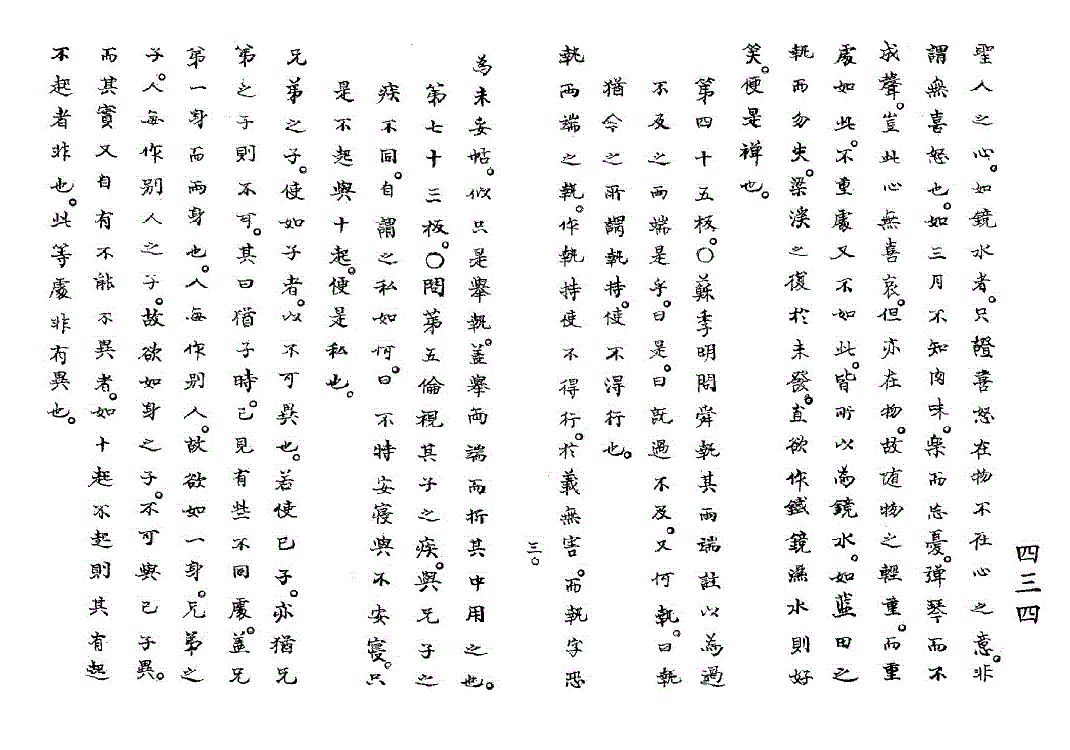 圣人之心。如镜水者。只證喜怒在物不在心之意。非谓无喜怒也。如三月不知肉味。乐而忘忧。弹琴而不成声。岂此心无喜哀。但亦在物。故随物之轻重。而重处如此。不重处又不如此。皆所以为镜水。如蓝田之执而勿失。梁溪之复于未发。直欲作铁镜湿水则好笑。便是禅也。
圣人之心。如镜水者。只證喜怒在物不在心之意。非谓无喜怒也。如三月不知肉味。乐而忘忧。弹琴而不成声。岂此心无喜哀。但亦在物。故随物之轻重。而重处如此。不重处又不如此。皆所以为镜水。如蓝田之执而勿失。梁溪之复于未发。直欲作铁镜湿水则好笑。便是禅也。第四十五板○苏季明问舜执其两端注以为过不及之两端是乎。曰是。曰既过不及。又何执。曰执犹今之所谓执持。使不得行也。
执两端之执。作执持使不得行。于义无害。而执字恐为未妥帖。似只是举执。盖举两端而折其中用之也。
第七十三板○问第五伦视其子之疾。与兄子之疾不同。自谓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寝与不安寝。只是不起与十起。便是私也。
兄弟之子。使如子者。以不可异也。若使己子。亦犹兄弟之子则不可。其曰犹子时。已见有些不同处。盖兄弟一身而两身也。人每作别人。故欲如一身。兄弟之子。人每作别人之子。故欲如身之子。不可与己子异。而其实又自有不能不异者。如十起不起则其有起不起者非也。此等处非有异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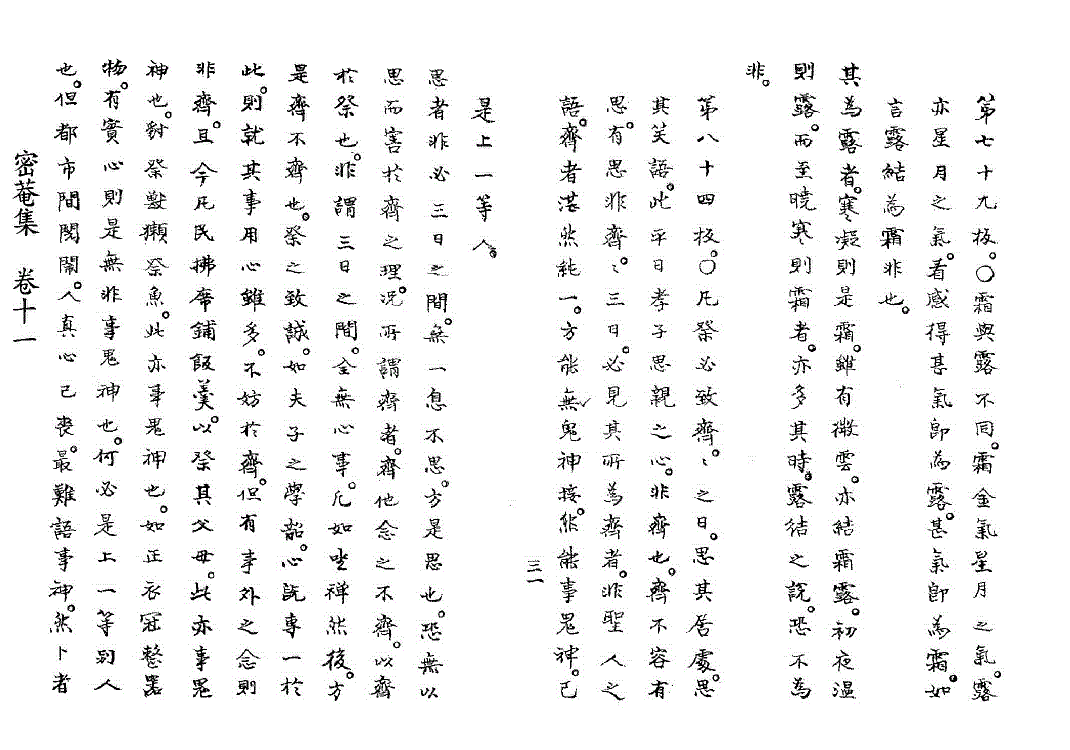 第七十九板○霜与露不同。霜金气星月之气。露亦星月之气。看感得甚气即为露。甚气即为霜。如言露结为霜非也。
第七十九板○霜与露不同。霜金气星月之气。露亦星月之气。看感得甚气即为露。甚气即为霜。如言露结为霜非也。其为露者。寒凝则是霜。虽有微云。亦结霜露。初夜温则露。而至晓寒则霜者。亦多其时。露结之说。恐不为非。
第八十四板○凡祭必致齐。齐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此平日孝子思亲之心。非齐也。齐不容有思。有思非齐。齐三日。必见其所为齐者。非圣人之语。齐者湛然纯一。方能无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思者非必三日之间。无一息不思。方是思也。恐无以思而害于齐之理。况所谓齐者。齐他念之不齐。以齐于祭也。非谓三日之间。全无心事。凡如坐禅然后。方是齐不齐也。祭之致诚。如夫子之学韶。心既专一于此。则就其事用心虽多。不妨于齐。但有事外之念则非齐。且今凡民拂席铺饭羹。以祭其父母。此亦事鬼神也。豺祭兽獭祭鱼。此亦事鬼神也。如正衣冠整器物。有实心则是无非事鬼神也。何必是上一等别人也。但都市间关闹。人真心已丧。最难语事神。然卜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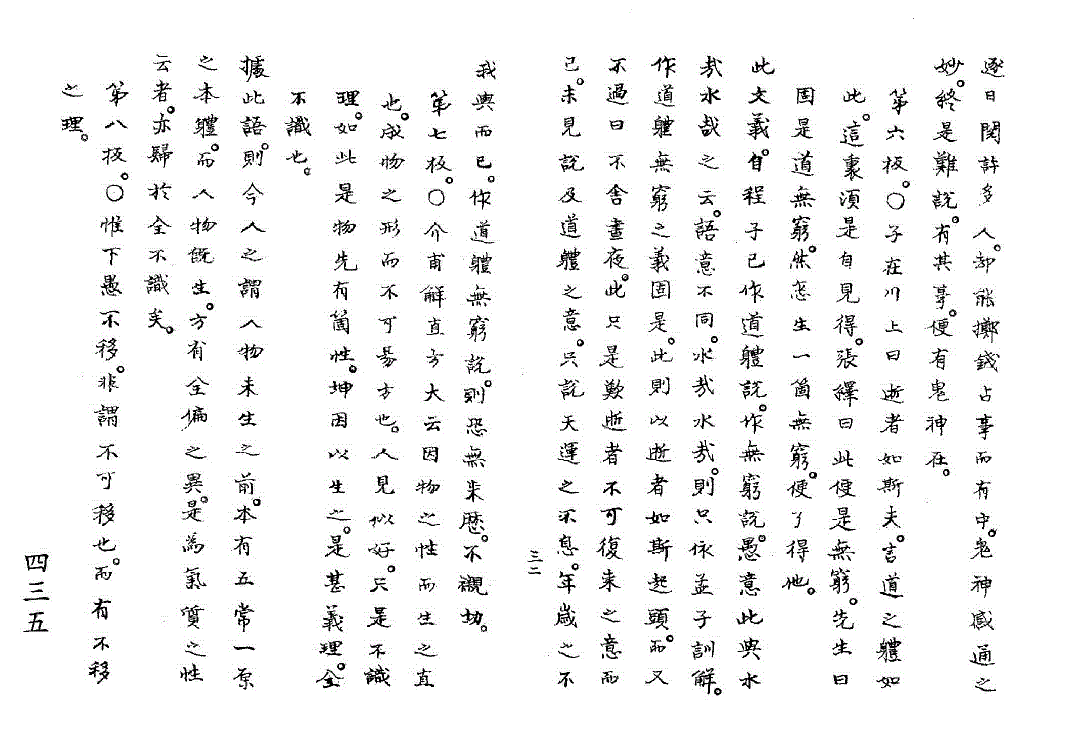 逐日关许多人。却能掷钱占事而有中。鬼神感通之妙。终是难说。有其事。便有鬼神在。
逐日关许多人。却能掷钱占事而有中。鬼神感通之妙。终是难说。有其事。便有鬼神在。第六板○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体如此。这里须是自见得。张绎曰此便是无穷。先生曰固是道无穷。然怎生一个无穷。便了得他。
此文义。自程子已作道体说。作无穷说。愚意此与水哉水哉之云。语意不同。水哉水哉。则只依孟子训解。作道体无穷之义固是。此则以逝者如斯起头。而又不过曰不舍昼夜。此只是叹逝者不可复来之意而已。未见说及道体之意。只说天运之不息。年岁之不我与而已。作道体无穷说。则恐无来历。不衬切。
第七板○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以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
据此语。则今人之谓人物未生之前。本有五常一原之本体。而人物既生。方有全偏之异。是为气质之性云者。亦归于全不识矣。
第八板○惟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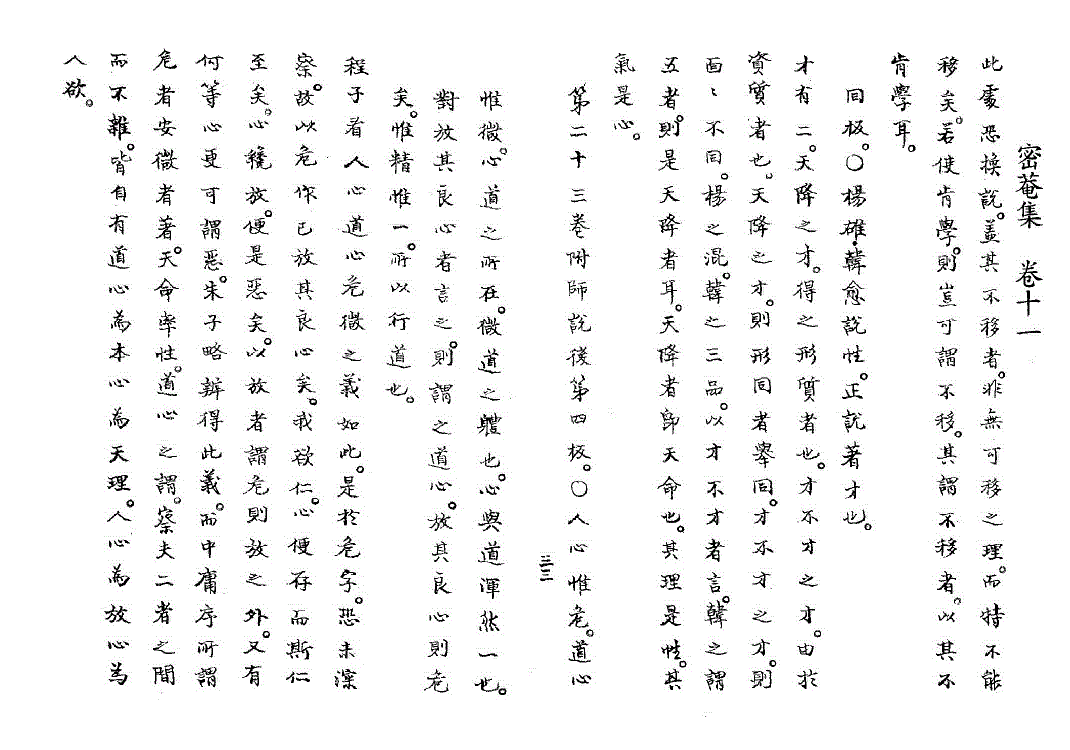 此处恐换说。盖其不移者。非无可移之理。而特不能移矣。若使肯学。则岂可谓不移。其谓不移者。以其不肯学耳。
此处恐换说。盖其不移者。非无可移之理。而特不能移矣。若使肯学。则岂可谓不移。其谓不移者。以其不肯学耳。同板○杨雄,韩愈说性。正说著才也。
才有二。天降之才。得之形质者也。才不才之才。由于资质者也。天降之才。则形同者举同。才不才之才。则面面不同。杨之混。韩之三品。以才不才者言。韩之谓五者。则是天降者耳。天降者即天命也。其理是性。其气是心。
第二十三卷附师说后第四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心与道浑然一也。对放其良心者言之。则谓之道心。放其良心则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程子看人心道心危微之义如此。是于危字。恐未深察。故以危作已放其良心矣。我欲仁。心便存而斯仁至矣。心才放。便是恶矣。以放者谓危则放之外。又有何等心更可谓恶。朱子略辨得此义。而中庸序所谓危者安微者著。天命率性。道心之谓。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皆自有道心为本心为天理。人心为放心为人欲。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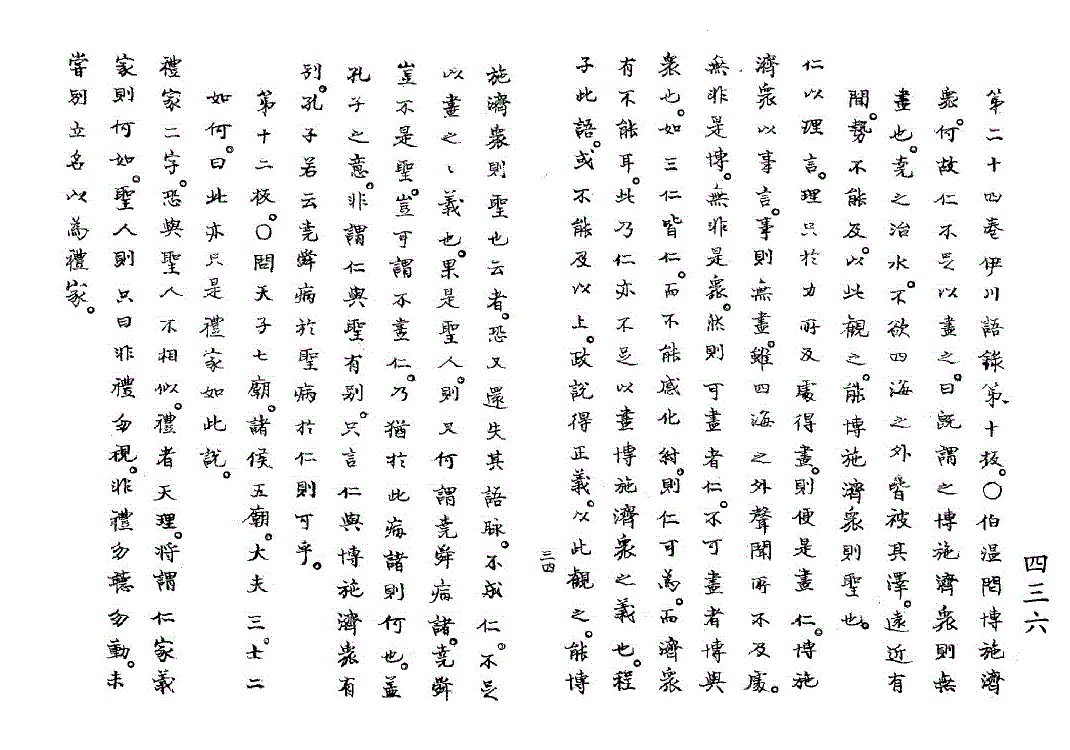 第二十四卷伊川语录第十板○伯温问博施济众。何故仁不足以尽之。曰既谓之博施济众则无尽也。尧之治水。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泽。远近有间。势不能及。以此观之。能博施济众则圣也。
第二十四卷伊川语录第十板○伯温问博施济众。何故仁不足以尽之。曰既谓之博施济众则无尽也。尧之治水。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泽。远近有间。势不能及。以此观之。能博施济众则圣也。仁以理言。理只于力所及处得尽。则便是尽仁。博施济众以事言。事则无尽。虽四海之外声闻所不及处。无非是博。无非是众。然则可尽者仁。不可尽者博与众也。如三仁皆仁。而不能感化纣。则仁可为。而济众有不能耳。此乃仁亦不足以尽博施济众之义也。程子此语。或不能及以上。政说得正义。以此观之。能博施济众则圣也云者。恐又还失其语脉。不成仁。不足以尽之之义也。果是圣人。则又何谓尧舜病诸。尧舜岂不是圣。岂可谓不尽仁。乃犹于此病诸则何也。盖孔子之意。非谓仁与圣有别。只言仁与博施济众有别。孔子若云尧舜病于圣病于仁则可乎。
第十二板○问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礼家如此说。
礼家二字。恐与圣人不相似。礼者天理。将谓仁家义家则何如。圣人则只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勿动。未尝别立名以为礼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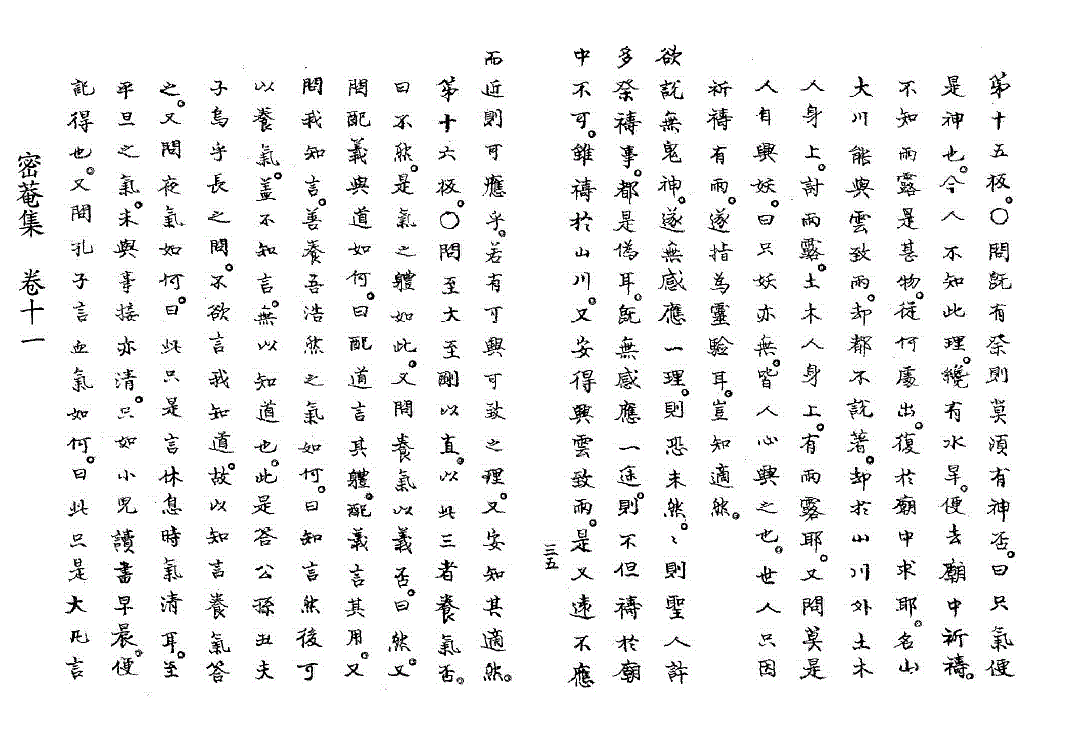 第十五板○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庙中祈祷。不知雨露是甚物。从何处出。复于庙中求耶。名山大川能与云致雨。却都不说著。却于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讨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问莫是人自兴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兴之也。世人只因祈祷有雨。遂指为灵验耳。岂知适然。
第十五板○问既有祭则莫须有神否。曰只气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庙中祈祷。不知雨露是甚物。从何处出。复于庙中求耶。名山大川能与云致雨。却都不说著。却于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讨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问莫是人自兴妖。曰只妖亦无。皆人心兴之也。世人只因祈祷有雨。遂指为灵验耳。岂知适然。欲说无鬼神。遂无感应一理。则恐未然。然则圣人许多祭祷事。都是伪耳。既无感应一途。则不但祷于庙中不可。虽祷于山川。又安得兴云致雨。是又远不应而近则可应乎。若有可兴可致之理。又安知其适然。
第十六板○问至大至刚以直。以此三者养气否。曰不然。是气之体如此。又问养气以义否。曰然。又问配义与道如何。曰配道言其体。配义言其用。又问我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如何。曰知言然后可以养气。盖不知言。无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孙丑夫子乌乎长之问。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养气答之。又问夜气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时气清耳。至平旦之气。未与事接亦清。只如小儿读书早晨。便记得也。又问孔子言血气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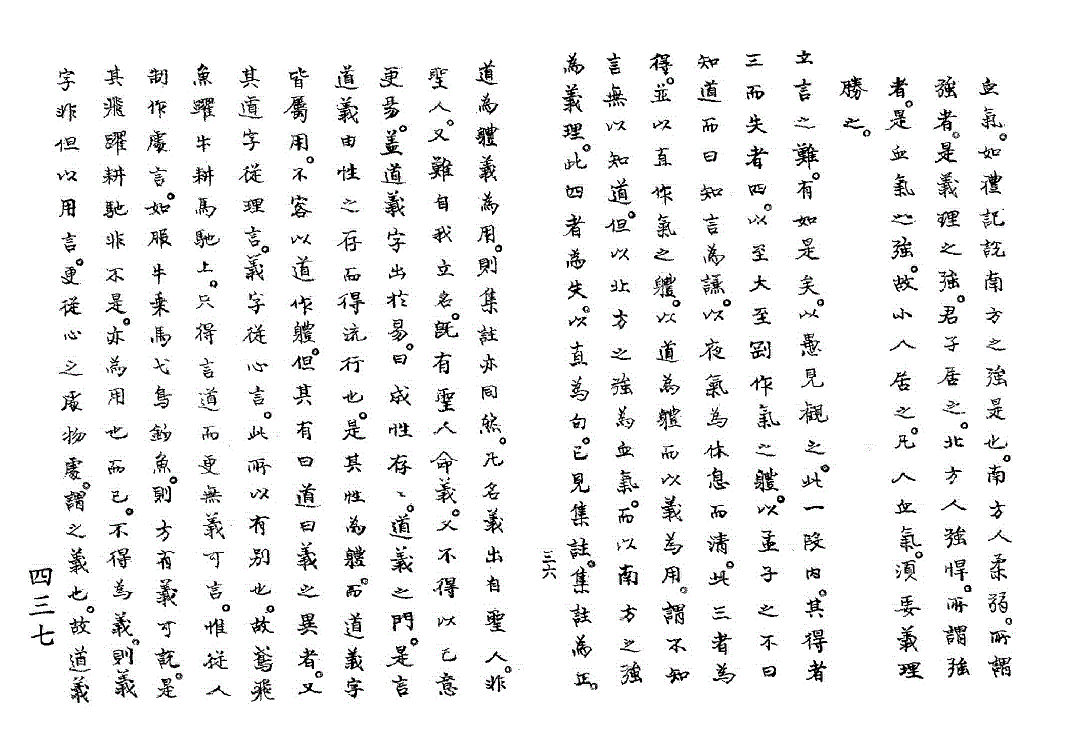 血气。如礼记说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义理之强。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须要义理胜之。
血气。如礼记说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谓强者。是义理之强。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谓强者。是血气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气。须要义理胜之。立言之难。有如是矣。以愚见观之。此一段内。其得者三而失者四。以至大至刚作气之体。以孟子之不曰知道而曰知言为谦。以夜气为休息而清。此三者为得。并以直作气之体。以道为体而以义为用。谓不知言无以知道。但以北方之强为血气。而以南方之强为义理。此四者为失。以直为句。已见集注。集注为正。道为体义为用。则集注亦同然。凡名义出自圣人。非圣人。又难自我立名。既有圣人命义。又不得以己意更易。盖道义字出于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是言道义由性之存而得流行也。是其性为体。而道义字皆属用。不容以道作体。但其有曰道曰义之异者。又其道字从理言。义字从心言。此所以有别也。故鸢飞鱼跃牛耕马驰上。只得言道而更无义可言。惟从人制作处言。如服牛乘马弋鸟钓鱼。则方有义可说。是其飞跃耕驰非不是。亦为用也而已。不得为义。则义字非但以用言。更从心之处物处。谓之义也。故道义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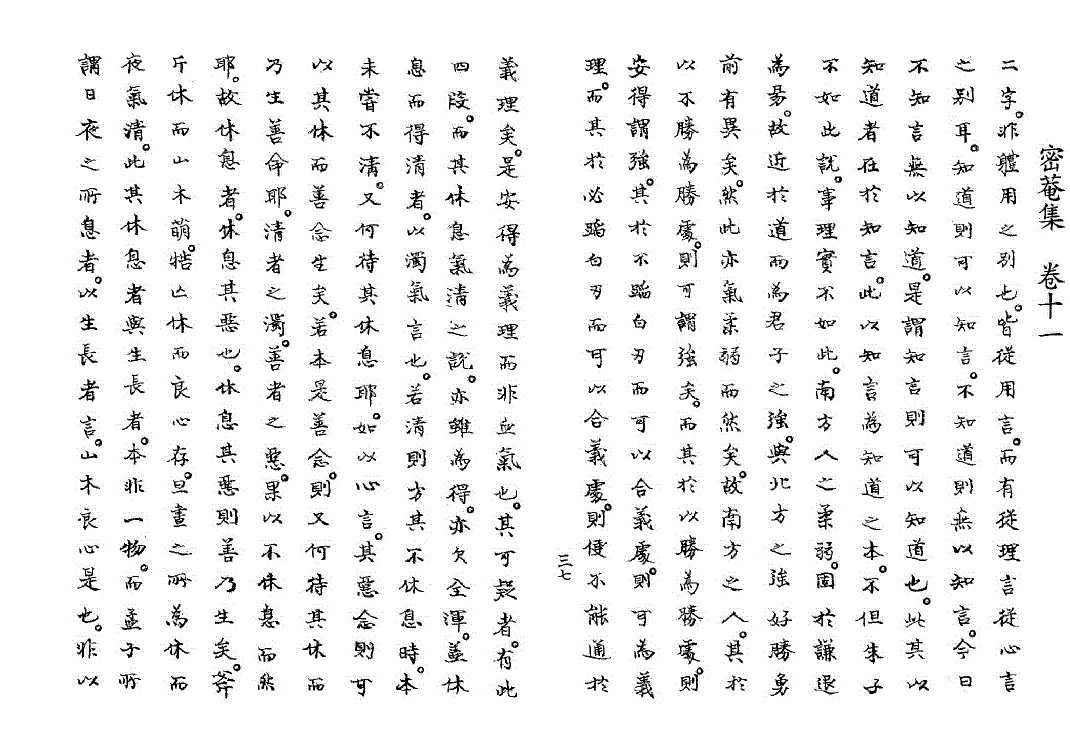 二字。非体用之别也。皆从用言。而有从理言从心言之别耳。知道则可以知言。不知道则无以知言。今曰不知言无以知道。是谓知言则可以知道也。此其以知道者在于知言。此以知言为知道之本。不但朱子不如此说。事理实不如此。南方人之柔弱。固于谦退为易。故近于道而为君子之强。与北方之强好胜勇前有异矣。然此亦气柔弱而然矣。故南方之人。其于以不胜为胜处。则可谓强矣。而其于以胜为胜处。则安得谓强。其于不蹈白刃而可以合义处。则可为义理。而其于必蹈白刃而可以合义处。则便不能通于义理矣。是安得为义理而非血气也。其可疑者。有此四段。而其休息气清之说。亦虽为得。亦欠全浑。盖休息而得清者。以浊气言也。若清则方其不休息时。本未尝不清。又何待其休息耶。如以心言。其恶念则可以其休而善念生矣。若本是善念。则又何待其休而乃生善命耶。清者之浊。善者之恶。果以不休息而然耶。故休息者。休息其恶也。休息其恶则善乃生矣。斧斤休而山木萌。牿亡休而良心存。旦昼之所为休而夜气清。此其休息者与生长者。本非一物。而孟子所谓日夜之所息者。以生长者言。山木良心是也。非以
二字。非体用之别也。皆从用言。而有从理言从心言之别耳。知道则可以知言。不知道则无以知言。今曰不知言无以知道。是谓知言则可以知道也。此其以知道者在于知言。此以知言为知道之本。不但朱子不如此说。事理实不如此。南方人之柔弱。固于谦退为易。故近于道而为君子之强。与北方之强好胜勇前有异矣。然此亦气柔弱而然矣。故南方之人。其于以不胜为胜处。则可谓强矣。而其于以胜为胜处。则安得谓强。其于不蹈白刃而可以合义处。则可为义理。而其于必蹈白刃而可以合义处。则便不能通于义理矣。是安得为义理而非血气也。其可疑者。有此四段。而其休息气清之说。亦虽为得。亦欠全浑。盖休息而得清者。以浊气言也。若清则方其不休息时。本未尝不清。又何待其休息耶。如以心言。其恶念则可以其休而善念生矣。若本是善念。则又何待其休而乃生善命耶。清者之浊。善者之恶。果以不休息而然耶。故休息者。休息其恶也。休息其恶则善乃生矣。斧斤休而山木萌。牿亡休而良心存。旦昼之所为休而夜气清。此其休息者与生长者。本非一物。而孟子所谓日夜之所息者。以生长者言。山木良心是也。非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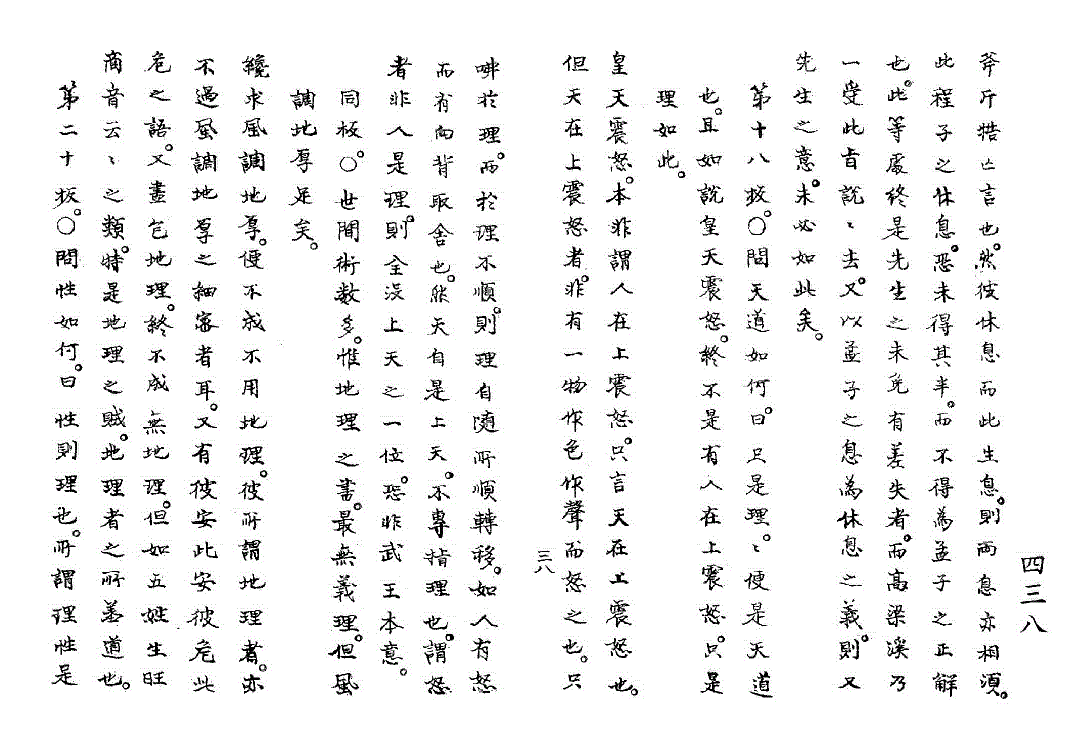 斧斤牿亡言也。然彼休息而此生息。则两息亦相须。此程子之休息。恐未得其半。而不得为孟子之正解也。此等处终是先生之未免有差失者。而高梁溪乃一受此旨说说去。又以孟子之息为休息之义。则又先生之意。未必如此矣。
斧斤牿亡言也。然彼休息而此生息。则两息亦相须。此程子之休息。恐未得其半。而不得为孟子之正解也。此等处终是先生之未免有差失者。而高梁溪乃一受此旨说说去。又以孟子之息为休息之义。则又先生之意。未必如此矣。第十八板○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皇天震怒。本非谓人在上震怒。只言天在上震怒也。但天在上震怒者。非有一物作色作声而怒之也。只咈于理。而于理不顺。则理自随所顺转移。如人有怒而有向背取舍也。然天自是上天。不专指理也。谓怒者非人是理。则全没上天之一位。恐非武王本意。
同板○世间术数多。惟地理之书。最无义理。但风调地厚足矣。
才求风调地厚。便不成不用地理。彼所谓地理者。亦不过风调地厚之细密者耳。又有彼安此安彼危此危之语。又尽包地理。终不成无地理。但如五姓生旺商音云云之类。特是地理之贼。地理者之所羞道也。
第二十板○问性如何。曰性则理也。所谓理性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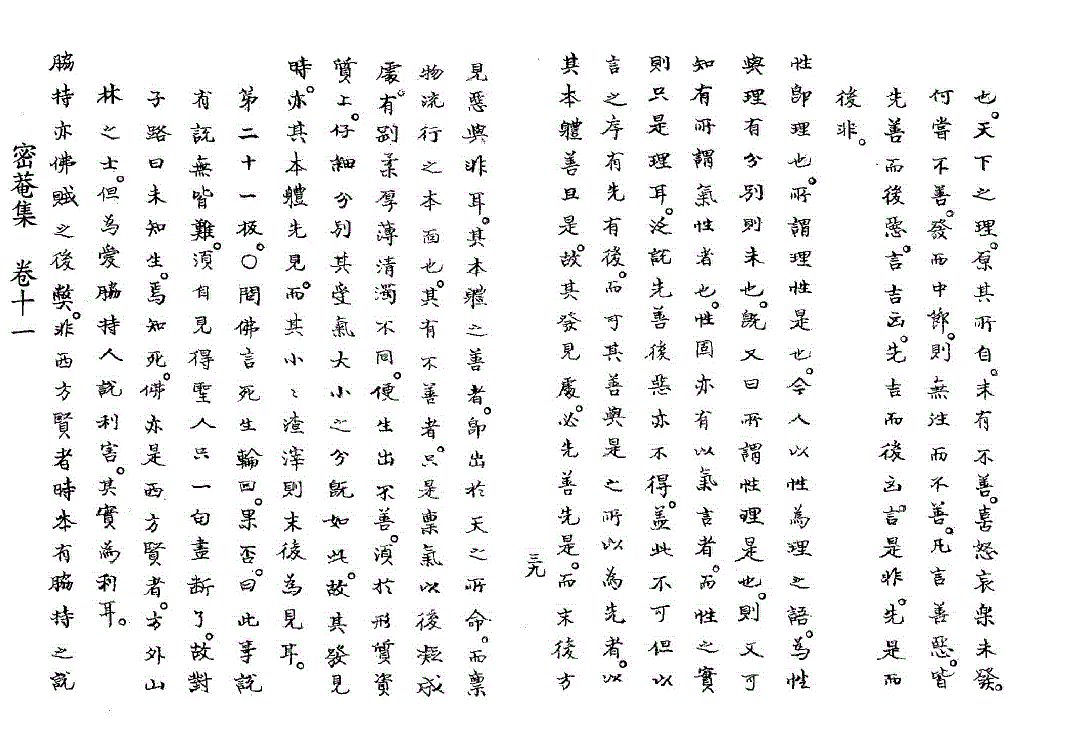 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先吉而后凶。言是非。先是而后非。
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先吉而后凶。言是非。先是而后非。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今人以性为理之语。为性与理有分别则未也。既又曰所谓性理是也。则又可知有所谓气性者也。性固亦有以气言者。而性之实则只是理耳。泛说先善后恶亦不得。盖此不可但以言之序有先有后。而可其善与是之所以为先者。以其本体善且是。故其发见处。必先善先是。而末后方见恶与非耳。其本体之善者。即出于天之所命。而禀物流行之本面也。其有不善者。只是禀气以后凝成处。有刚柔厚薄清浊不同。便生出不善。须于形质资质上。仔细分别其受气大小之分既如此。故其发见时。亦其本体先见。而其小小渣滓则末后为见耳。
第二十一板○问佛言死生轮回。果否。曰此事说有说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一句尽断了。故对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贤者。方外山林之士。但为爱胁持人说利害。其实为利耳。
胁持亦佛贼之后弊。非西方贤者时本有胁持之说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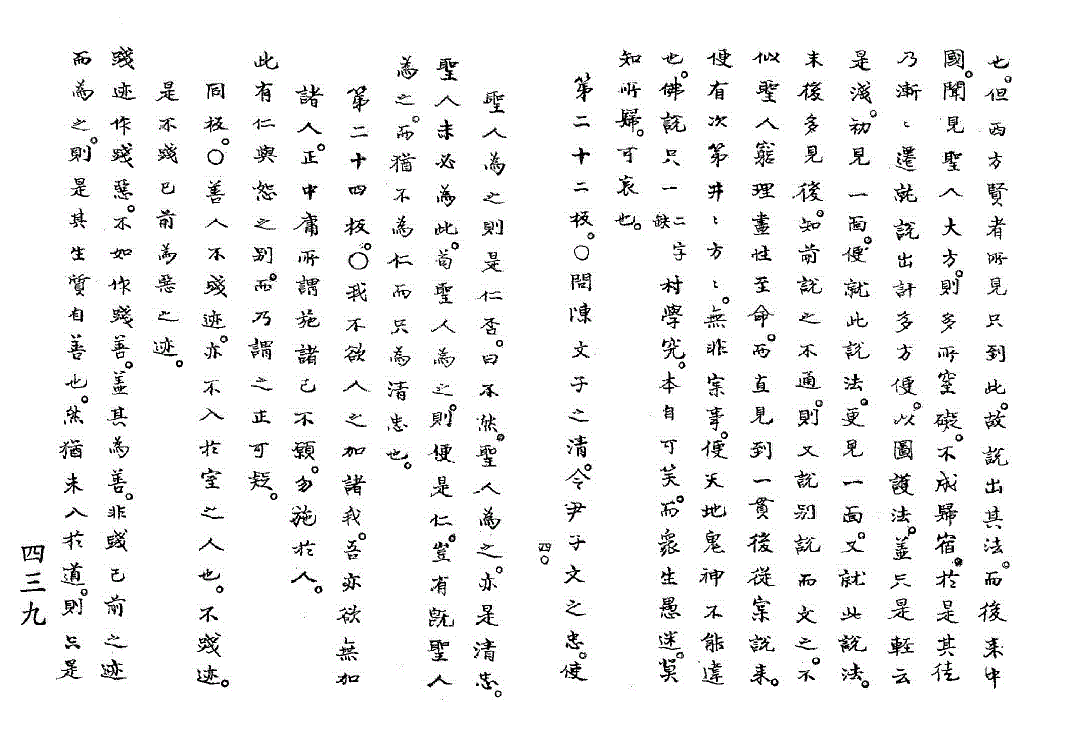 也。但西方贤者所见只到此。故说出其法。而后来中国。闻见圣人大方。则多所窒碍。不成归宿。于是其徒乃渐渐迁就说出计多方便。以图护法。盖只是轻云是浅。初见一面。便就此说法。更见一面。又就此说法。末后多见后。知前说之不通。则又说别说而文之。不似圣人穷理尽性至命。而直见到一贯后从宲说来。便有次第井井方方。无非宲事。便天地鬼神不能违也。佛说只一(二字缺)村学究。本自可笑。而众生愚迷。莫知所归。可哀也。
也。但西方贤者所见只到此。故说出其法。而后来中国。闻见圣人大方。则多所窒碍。不成归宿。于是其徒乃渐渐迁就说出计多方便。以图护法。盖只是轻云是浅。初见一面。便就此说法。更见一面。又就此说法。末后多见后。知前说之不通。则又说别说而文之。不似圣人穷理尽性至命。而直见到一贯后从宲说来。便有次第井井方方。无非宲事。便天地鬼神不能违也。佛说只一(二字缺)村学究。本自可笑。而众生愚迷。莫知所归。可哀也。第二十二板○问陈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圣人为之则是仁否。曰不然。圣人为之。亦是清忠。
圣人未必为此。苟圣人为之。则便是仁。岂有既圣人为之。而犹不为仁而只为清忠也。
第二十四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正中庸所谓施诸己不愿。勿施于人。
此有仁与恕之别。而乃谓之正可疑。
同板○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之人也。不践迹。是不践已前为恶之迹。
践迹作践恶。不如作践善。盖其为善。非践已前之迹而为之。则是其生质自善也。然犹未入于道。则只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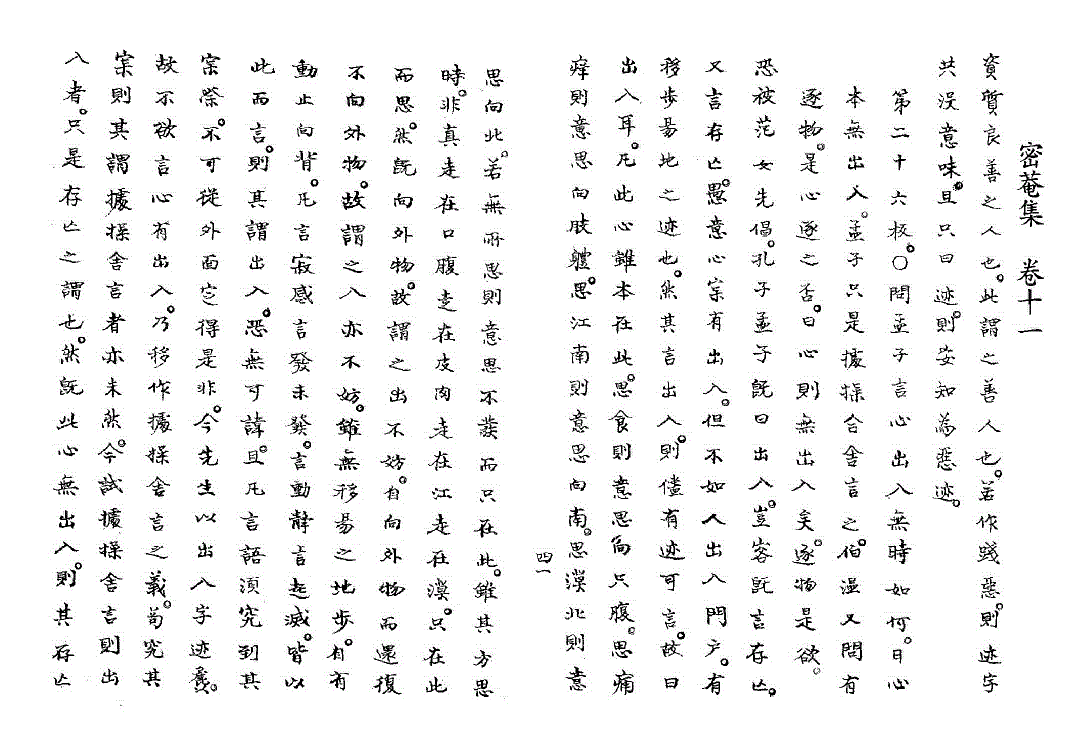 资质良善之人也。此谓之善人也。若作践恶。则迹字共没意味。且只曰迹。则安知为恶迹。
资质良善之人也。此谓之善人也。若作践恶。则迹字共没意味。且只曰迹。则安知为恶迹。第二十六板○问孟子言心出入无时如何。曰心本无出入。孟子只是据操合舍言之。伯温又问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则无出入矣。逐物是欲。
恐被范女先倡。孔子孟子既曰出入。岂容既言存亡。又言存亡。愚意心宲有出入。但不如人出入门户。有移步易地之迹也。然其言出入。则尽有迹可言。故曰出入耳。凡此心虽本在此。思食则意思向只腹。思痛痒则意思向肢体。思江南则意思向南。思漠北则意思向北。若无所思则意思不发而只在此。虽其方思时。非真走在口腹走在皮肉走在江走在漠。只在此而思。然既向外物。故谓之出不妨。自向外物而还复不向外物。故谓之入亦不妨。虽无移易之地步。自有动止向背。凡言寂感言发未发。言动静言起灭。皆以此而言。则其谓出入。恐无可讳。且凡言语须究到其宲际。不可从外面定得是非。今先生以出入字迹粗。故不欲言心有出入。乃移作据操舍言之义。苟究其宲则其谓据操舍言者亦未然。今试据操舍言则出入者。只是存亡之谓也。然既此心无出入。则其存亡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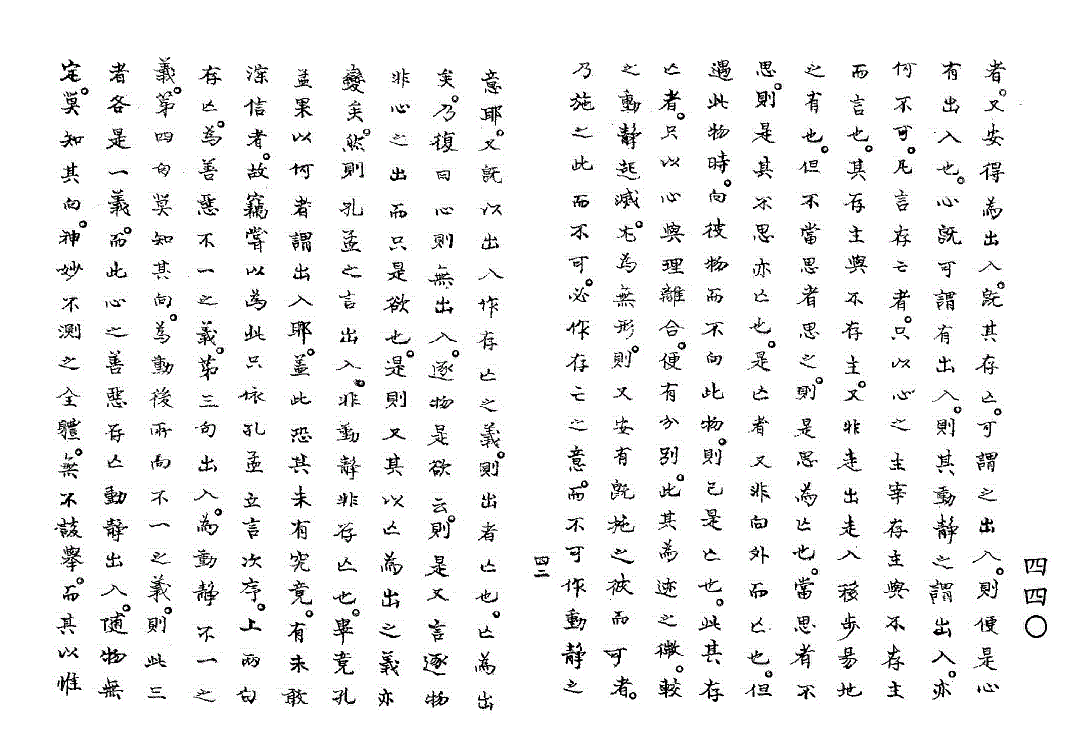 者。又安得为出入。既其存亡。可谓之出入。则便是心有出入也。心既可谓有出入。则其动静之谓出入。亦何不可。凡言存亡者。只以心之主宰存主与不存主而言也。其存主与不存主。又非走出走入移步易地之有也。但不当思者思之。则是思为亡也。当思者不思。则是其不思亦亡也。是亡者又非向外而亡也。但遇此物时。向彼物而不向此物。则已是亡也。此其存亡者。只以心与理离合。便有分别。此其为迹之微。较之动静起灭。尤为无形。则又安有既施之彼而可者。乃施之此而不可。必作存亡之意。而不可作动静之意耶。又既以出入作存亡之义。则出者亡也。亡为出矣。乃复曰心则无出入。逐物是欲云。则是又言逐物非心之出而只是欲也。是则又其以亡为出之义亦变矣。然则孔孟之言出入。非动静非存亡也。毕竟孔孟果以何者谓出入耶。盖此恐其未有究竟。有未敢深信者。故窃尝以为此只依孔孟立言次序。上两句存亡。为善恶不一之义。第三句出入。为动静不一之义。第四句莫知其向。为动后所向不一之义。则此三者各是一义。而此心之善恶存亡动静出入。随物无定。莫知其向。神妙不测之全体。无不该举。而其以惟
者。又安得为出入。既其存亡。可谓之出入。则便是心有出入也。心既可谓有出入。则其动静之谓出入。亦何不可。凡言存亡者。只以心之主宰存主与不存主而言也。其存主与不存主。又非走出走入移步易地之有也。但不当思者思之。则是思为亡也。当思者不思。则是其不思亦亡也。是亡者又非向外而亡也。但遇此物时。向彼物而不向此物。则已是亡也。此其存亡者。只以心与理离合。便有分别。此其为迹之微。较之动静起灭。尤为无形。则又安有既施之彼而可者。乃施之此而不可。必作存亡之意。而不可作动静之意耶。又既以出入作存亡之义。则出者亡也。亡为出矣。乃复曰心则无出入。逐物是欲云。则是又言逐物非心之出而只是欲也。是则又其以亡为出之义亦变矣。然则孔孟之言出入。非动静非存亡也。毕竟孔孟果以何者谓出入耶。盖此恐其未有究竟。有未敢深信者。故窃尝以为此只依孔孟立言次序。上两句存亡。为善恶不一之义。第三句出入。为动静不一之义。第四句莫知其向。为动后所向不一之义。则此三者各是一义。而此心之善恶存亡动静出入。随物无定。莫知其向。神妙不测之全体。无不该举。而其以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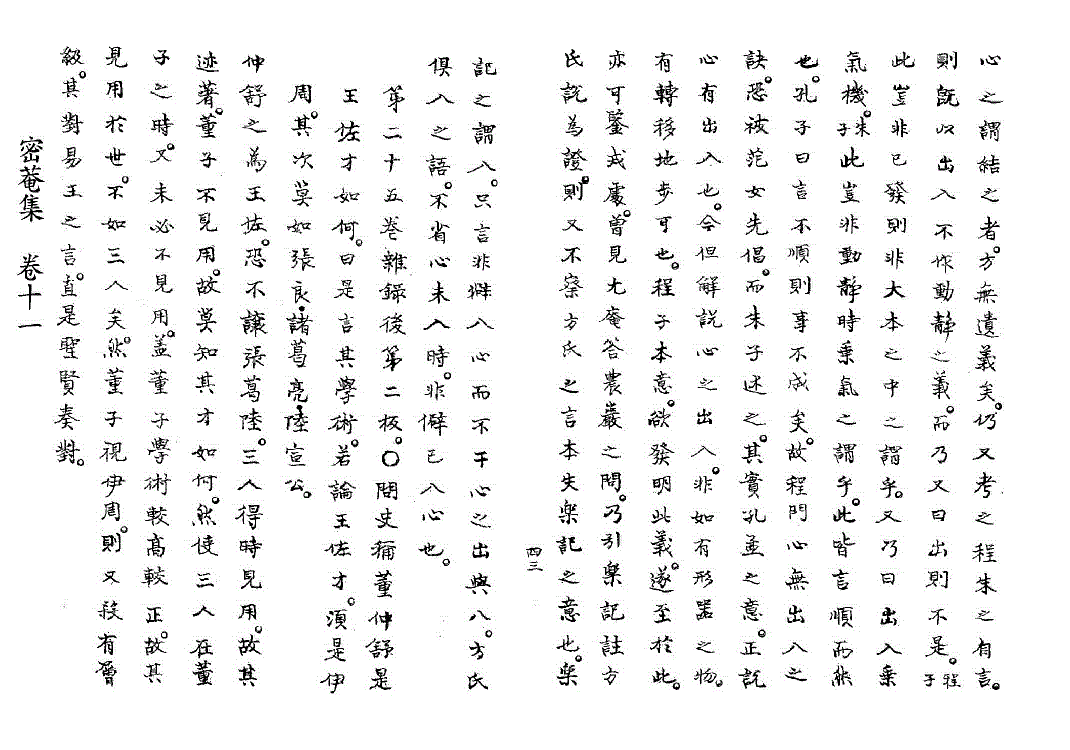 心之谓结之者。方无遗义矣。仍又考之程朱之自言。则既以出入不作动静之义。而乃又曰出则不是。(程子)此岂非已发则非大本之中之谓乎。又乃曰出入乘气机。(朱子)此岂非动静时乘气之谓乎。此皆言顺而然也。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矣。故程门心无出入之诀。恐被范女先倡。而朱子述之。其实孔孟之意。正说心有出入也。今但解说心之出入。非如有形器之物。有转移地步可也。程子本意。欲发明此义。遂至于此。亦可鉴戒处。曾见尤庵答农岩之问。乃引乐记注方氏说为證。则又不察方氏之言本失乐记之意也。乐记之谓入。只言非僻入心而不干心之出与入。方氏俱入之语。不省心未入时。非僻已入心也。
心之谓结之者。方无遗义矣。仍又考之程朱之自言。则既以出入不作动静之义。而乃又曰出则不是。(程子)此岂非已发则非大本之中之谓乎。又乃曰出入乘气机。(朱子)此岂非动静时乘气之谓乎。此皆言顺而然也。孔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矣。故程门心无出入之诀。恐被范女先倡。而朱子述之。其实孔孟之意。正说心有出入也。今但解说心之出入。非如有形器之物。有转移地步可也。程子本意。欲发明此义。遂至于此。亦可鉴戒处。曾见尤庵答农岩之问。乃引乐记注方氏说为證。则又不察方氏之言本失乐记之意也。乐记之谓入。只言非僻入心而不干心之出与入。方氏俱入之语。不省心未入时。非僻已入心也。第二十五卷杂录后第二板○问史称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是言其学术。若论王佐才。须是伊周。其次莫如张良,诸葛亮,陆宣公。
仲舒之为王佐。恐不让张,葛,陆。三人得时见用。故其迹著。董子不见用。故莫知其才如何。然使三人在董子之时。又未必不见用。盖董子学术较高较正。故其见用于世。不如三人矣。然董子视伊周。则又杀有层级。其对易王之言。直是圣贤奏对。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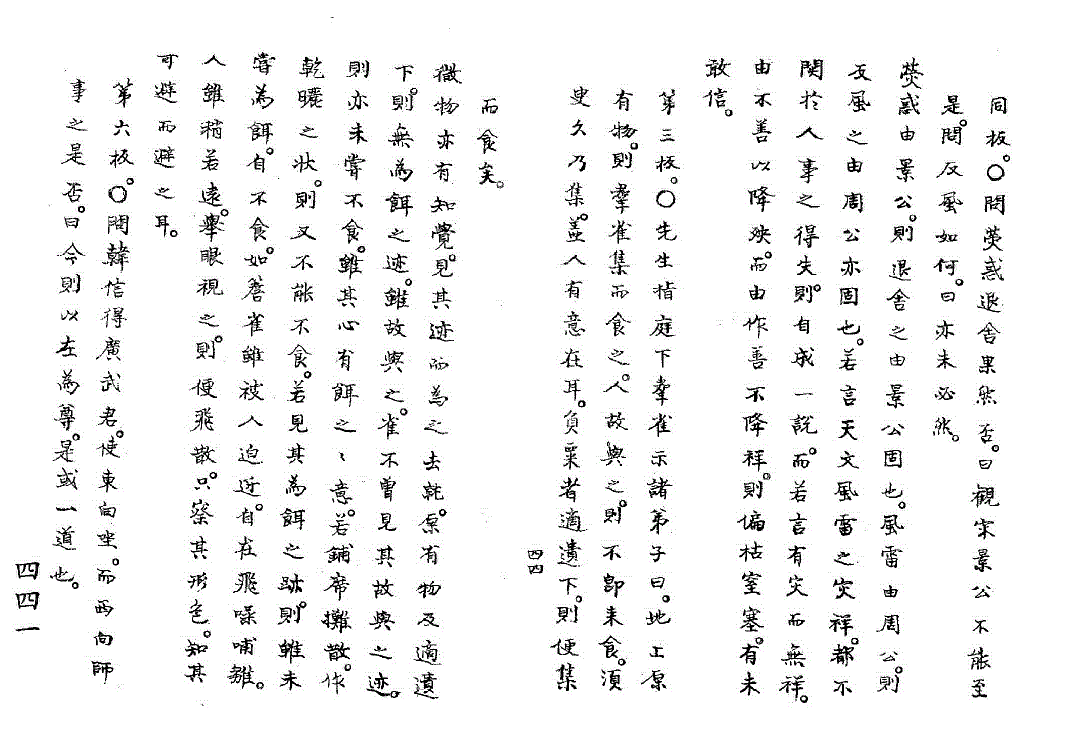 同板○问荧惑退舍果然否。曰观宋景公不能至是。问反风如何。曰亦未必然。
同板○问荧惑退舍果然否。曰观宋景公不能至是。问反风如何。曰亦未必然。荧惑由景公。则退舍之由景公固也。风雷由周公。则反风之由周公亦固也。若言天文风雷之灾祥。都不关于人事之得失。则自成一说。而若言有灾而无祥。由不善以降殃。而由作善不降祥。则偏枯窒塞。有未敢信。
第三板○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则群雀集而食之。人故与之。则不即来食。须臾久乃集。盖人有意在耳。负粟者适遗下。则便集而食矣。
微物亦有知觉。见其迹而为之去就。原有物及适遗下。则无为饵之迹。虽故与之。雀不曾见其故与之迹。则亦未尝不食。虽其心有饵之之意。若铺席摊散。作乾晒之状。则又不能不食。若见其为饵之迹。则虽未尝为饵。自不食。如檐雀虽被人迫近。自在飞噪哺雏。人虽稍若远。举眼视之。则便飞散。只察其形色。知其可避而避之耳。
第六板○问韩信得广武君。使东向坐。而西向师事之是否。曰今则以左为尊。是或一道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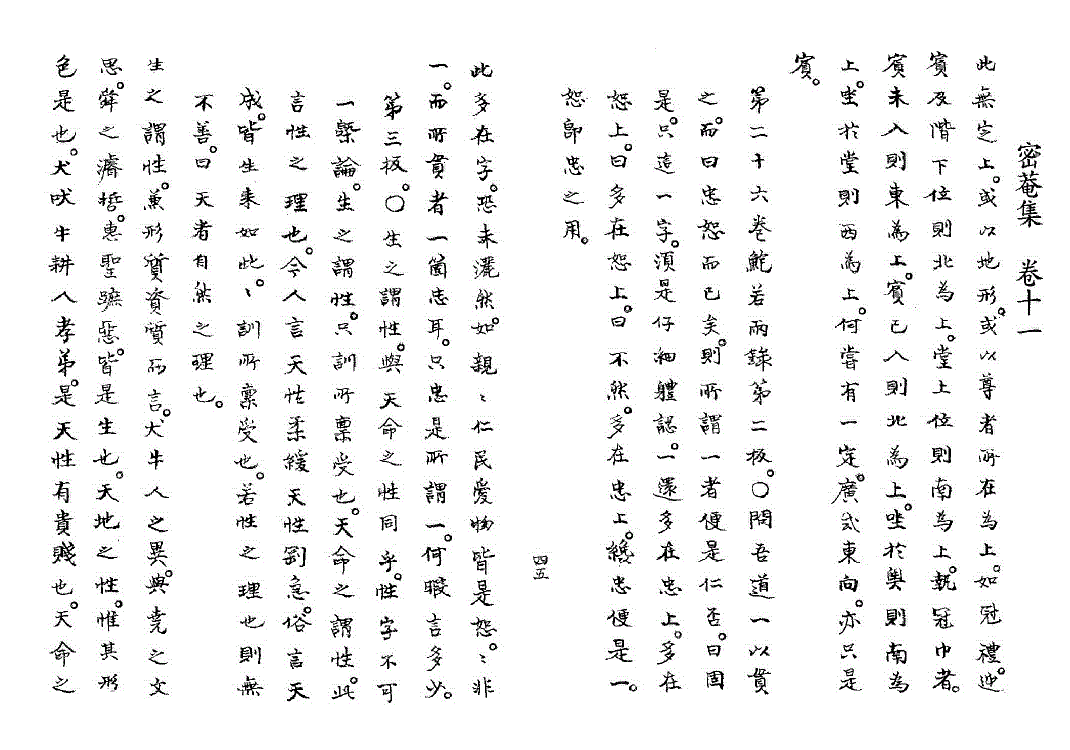 此无定上。或以地形。或以尊者所在为上。如冠礼。迎宾及阶下位则北为上。堂上位则南为上。执冠巾者。宾未入则东为上。宾已入则北为上。坐于奥则南为上。坐于堂则西为上。何尝有一定。广武东向。亦只是宾。
此无定上。或以地形。或以尊者所在为上。如冠礼。迎宾及阶下位则北为上。堂上位则南为上。执冠巾者。宾未入则东为上。宾已入则北为上。坐于奥则南为上。坐于堂则西为上。何尝有一定。广武东向。亦只是宾。第二十六卷鲍若雨录第二板○问吾道一以贯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则所谓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这一字。须是仔细体认。一还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才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
此多在字。恐未洒然。如亲亲仁民爱物皆是恕。恕非一。而所贯者一个忠耳。只忠是所谓一。何暇言多少。
第三板○生之谓性。与天命之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论。生之谓性。只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生之谓性。兼形质资质而言。犬牛人之异。与尧之文思。舜之浚哲。惠圣蹠恶。皆是生也。天地之性。惟其形色是也。犬吠牛耕人孝弟。是天性有贵贱也。天命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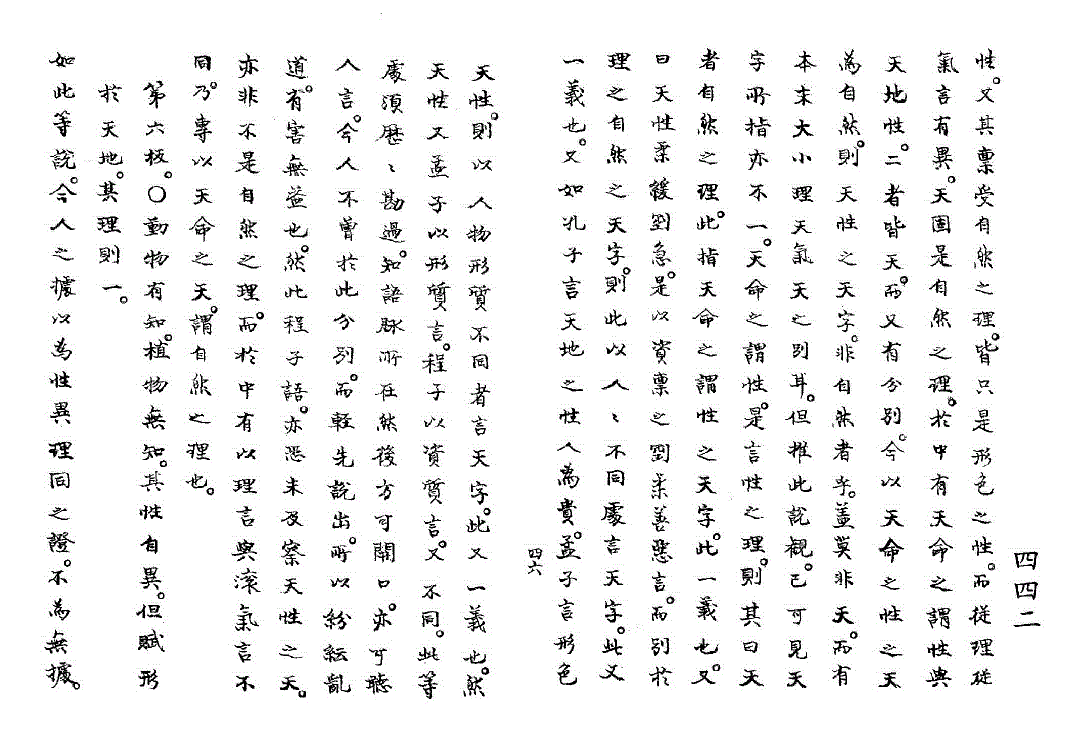 性。又其禀受自然之理。皆只是形色之性。而从理从气言有异。天固是自然之理。于中有天命之谓性与天地性。二者皆天。而又有分别。今以天命之性之天为自然。则天性之天字。非自然者乎。盖莫非天。而有本末大小理天气天之别耳。但推此说观。已可见天字所指亦不一。天命之谓性。是言性之理。则其曰天者自然之理。此指天命之谓性之天字。此一义也。又曰天性柔缓刚急。是以资禀之刚柔善恶言。而别于理之自然之天字。则此以人人不同处言天字。此又一义也。又如孔子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言形色天性。则以人物形质不同者言天字。此又一义也。然天性又孟子以形质言。程子以资质言。又不同。此等处须历历勘过。知语脉所在然后方可开口。亦可听人言。今人不曾于此分别。而轻先说出。所以纷纭乱道。有害无益也。然此程子语。亦恐未及察天性之天。亦非不是自然之理。而于中有以理言与滚气言不同。乃专以天命之天。谓自然之理也。
性。又其禀受自然之理。皆只是形色之性。而从理从气言有异。天固是自然之理。于中有天命之谓性与天地性。二者皆天。而又有分别。今以天命之性之天为自然。则天性之天字。非自然者乎。盖莫非天。而有本末大小理天气天之别耳。但推此说观。已可见天字所指亦不一。天命之谓性。是言性之理。则其曰天者自然之理。此指天命之谓性之天字。此一义也。又曰天性柔缓刚急。是以资禀之刚柔善恶言。而别于理之自然之天字。则此以人人不同处言天字。此又一义也。又如孔子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言形色天性。则以人物形质不同者言天字。此又一义也。然天性又孟子以形质言。程子以资质言。又不同。此等处须历历勘过。知语脉所在然后方可开口。亦可听人言。今人不曾于此分别。而轻先说出。所以纷纭乱道。有害无益也。然此程子语。亦恐未及察天性之天。亦非不是自然之理。而于中有以理言与滚气言不同。乃专以天命之天。谓自然之理也。第六板○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
如此等说。今人之据以为性异理同之證。不为无据。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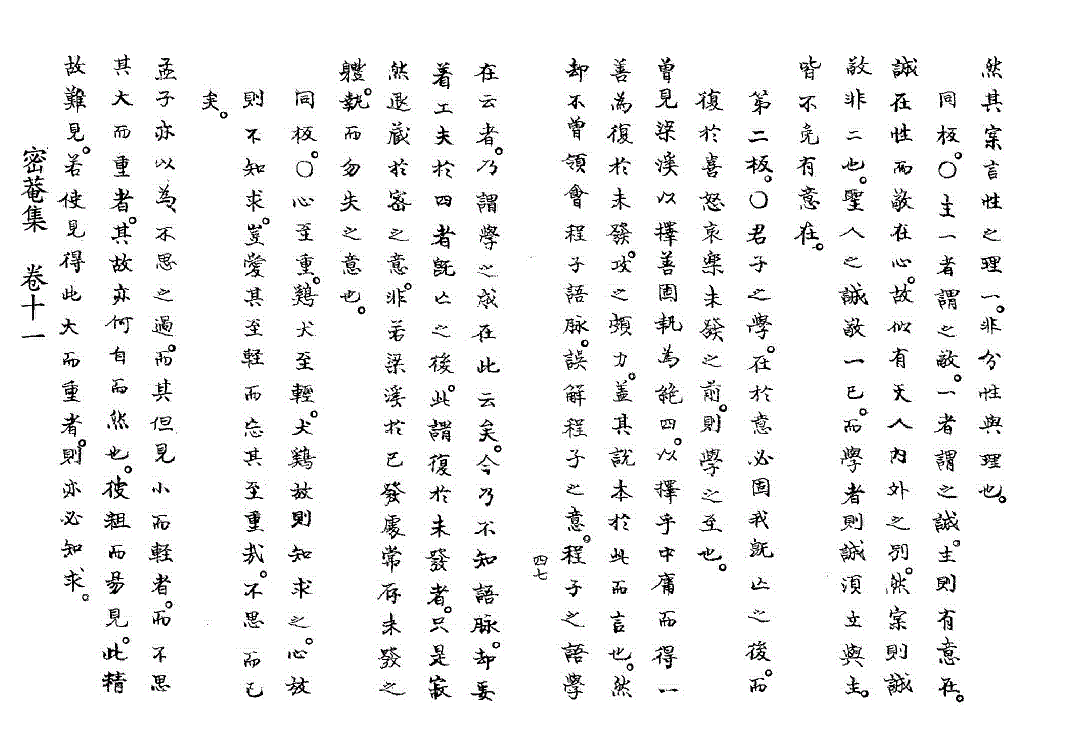 然其宲言性之理一。非分性与理也。
然其宲言性之理一。非分性与理也。同板○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主则有意在。
诚在性而敬在心。故似有天人内外之别。然宲则诚敬非二也。圣人之诚敬一已。而学者则诚须立与主。皆不免有意在。
第二板○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曾见梁溪以择善固执为绝四。以择乎中庸而得一善为复于未发。攻之颇力。盖其说本于此而言也。然却不曾领会程子语脉。误解程子之意。程子之语学在云者。乃谓学之成在此云矣。今乃不知语脉。却要着工夫于四者既亡之后。此谓复于未发者。只是寂然退藏于密之意。非若梁溪于已发处常存未发之体。执而勿失之意也。
同板○心至重。鸡犬至轻。犬鸡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不思而已矣。
孟子亦以为不思之过。而其但见小而轻者。而不思其大而重者。其故亦何自而然也。彼粗而易见。此精故难见。若使见得此大而重者。则亦必知求。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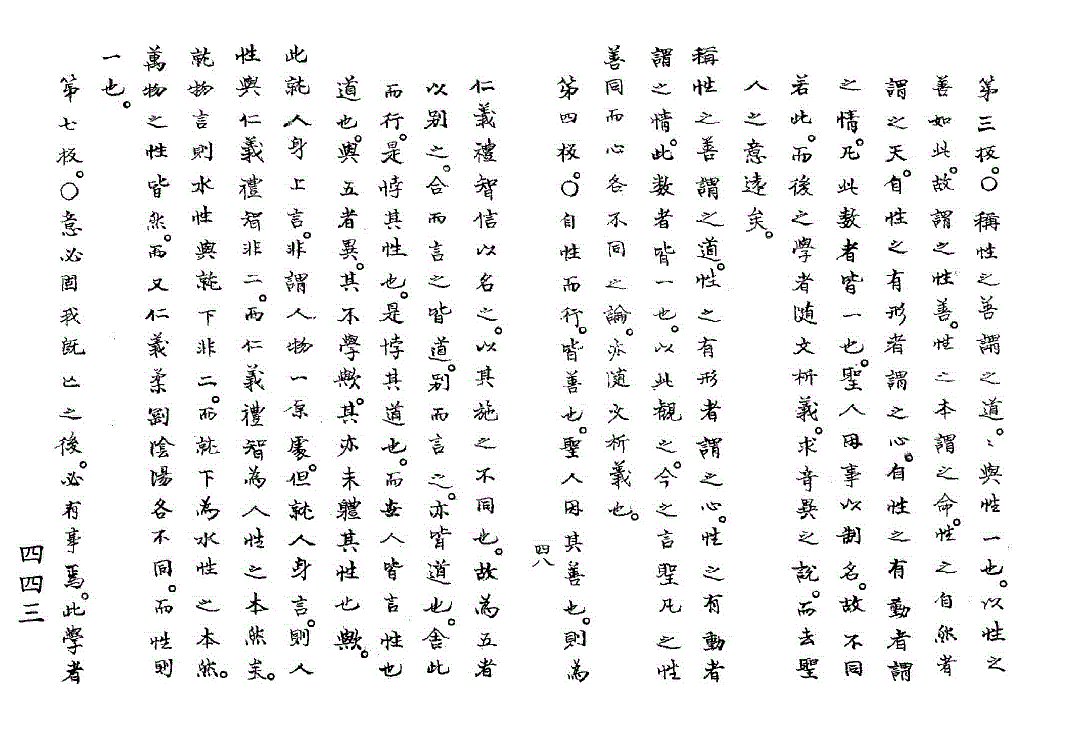 第三板○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远矣。
第三板○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远矣。称性之善谓之道。性之有形者谓之心。性之有动者谓之情。此数者皆一也。以此观之。今之言圣凡之性善同而心各不同之论。亦随文析义也。
第四板○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与五者异。其不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
此就人身上言。非谓人物一原处。但就人身言。则人性与仁义礼智非二。而仁义礼智为人性之本然矣。就物言则水性与就下非二。而就下为水性之本然。万物之性皆然。而又仁义柔刚阴阳各不同。而性则一也。
第七板○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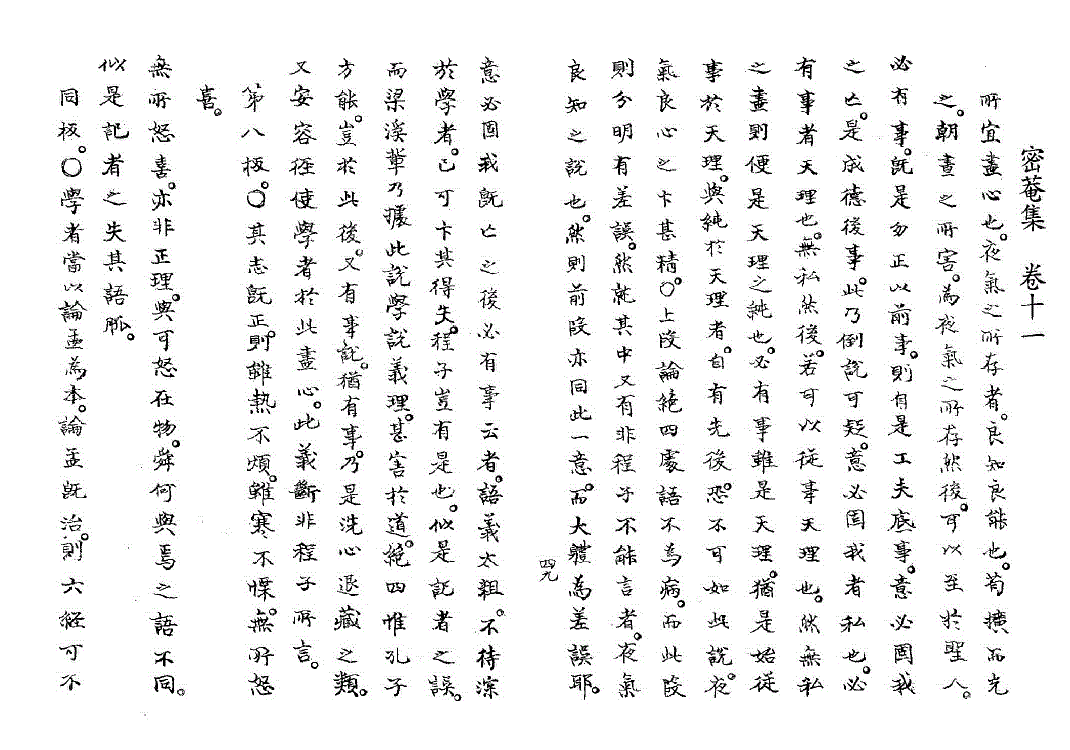 所宜尽心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苟扩而充之。朝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所宜尽心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苟扩而充之。朝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必有事。既是勿正以前事。则自是工夫底事。意必固我之亡。是成德后事。此乃倒说可疑。意必固我者私也。必有事者天理也。无私然后。若可以从事天理也。然无私之尽则便是天理之纯也。必有事虽是天理。犹是始从事于天理。与纯于天理者。自有先后。恐不可如此说。夜气良心之卞甚精。○上段论绝四处语不为病。而此段则分明有差误。然就其中又有非程子不能言者。夜气良知之说也。然则前段亦同此一意。而大体为差误耶。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云者。语义太粗。不待深于学者。已可卞其得失。程子岂有是也。似是记者之误。而梁溪辈乃据此说学说义理。甚害于道。绝四惟孔子方能。岂于此后。又有事说。犹有事。乃是洗心退藏之类。又安容径使学者于此尽心。此义断非程子所言。
第八板○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慄。无所怒喜。
无所怒喜。亦非正理。与可怒在物。舜何与焉之语不同。似是记者之失其语脉。
同板○学者当以论孟为本。论孟既治。则六经可不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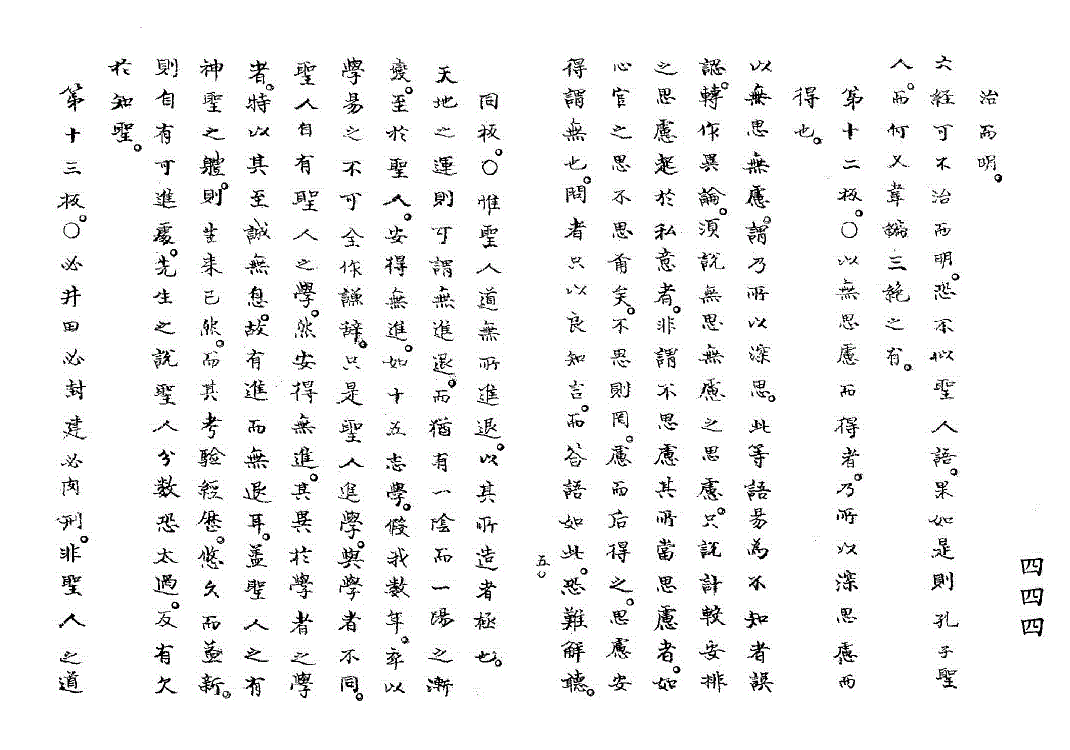 治而明。
治而明。六经可不治而明。恐不似圣人语。果如是则孔子圣人。而何又韦编三绝之有。
第十二板○以无思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虑而得也。
以无思无虑。谓乃所以深思。此等语易为不知者误认。转作异论。须说无思无虑之思虑。只说计较安排之思虑起于私意者。非谓不思虑其所当思虑者。如心官之思不思尔矣。不思则罔。虑而后得之。思虑安得谓无也。问者只以良知言。而答语如此。恐难解听。
同板○惟圣人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天地之运则可谓无进退。而犹有一阴而一阳之渐变。至于圣人。安得无进。如十五志学。假我数年。卒以学易之不可全作谦辞。只是圣人进学。与学者不同。圣人自有圣人之学。然安得无进。其异于学者之学者。特以其至诚无息。故有进而无退耳。盖圣人之有神圣之体。则生来已然。而其考验经历。悠久而益新。则自有可进处。先生之说圣人分数恐太过。反有欠于知圣。
第十三板○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5H 页
 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民不劳。放肉刑而行之。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
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民不劳。放肉刑而行之。民不怨。故善学者得圣人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饮食一也。必笾豆匙箸正席端坐先祭。乃饮食之。饮食一也。必毋放饭流歠。不如此则其道苟而不备。后必有悖德之事。愚意必井田必封建肉刑然后。乃道乃正。不然则苟而已。后必有弊。且此三者皆天经也。安得而易也。然皆王政也。有王者则不劳而行。无王者则虽劳而不行。程子之言。见其无王者也。然无王者则不但三者不行。虽放三者。亦无不病不劳不怨之理。阳春则冻融草生。穷阴则河水陨箨。其间相绝。意思不到。而皆一理一气。不容安排增损也。王政如风霆。无物不振动变化。有不动者。政有未尽耳。安有如此惫底王道。
第三十一卷朱公掞问学拾遗第二板○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
性与天道。非自得之则不知。故曰不可得而闻。重在闻字。非夫子不言也。
第三板○君子为善。只有上达。小人为不善。只有下达。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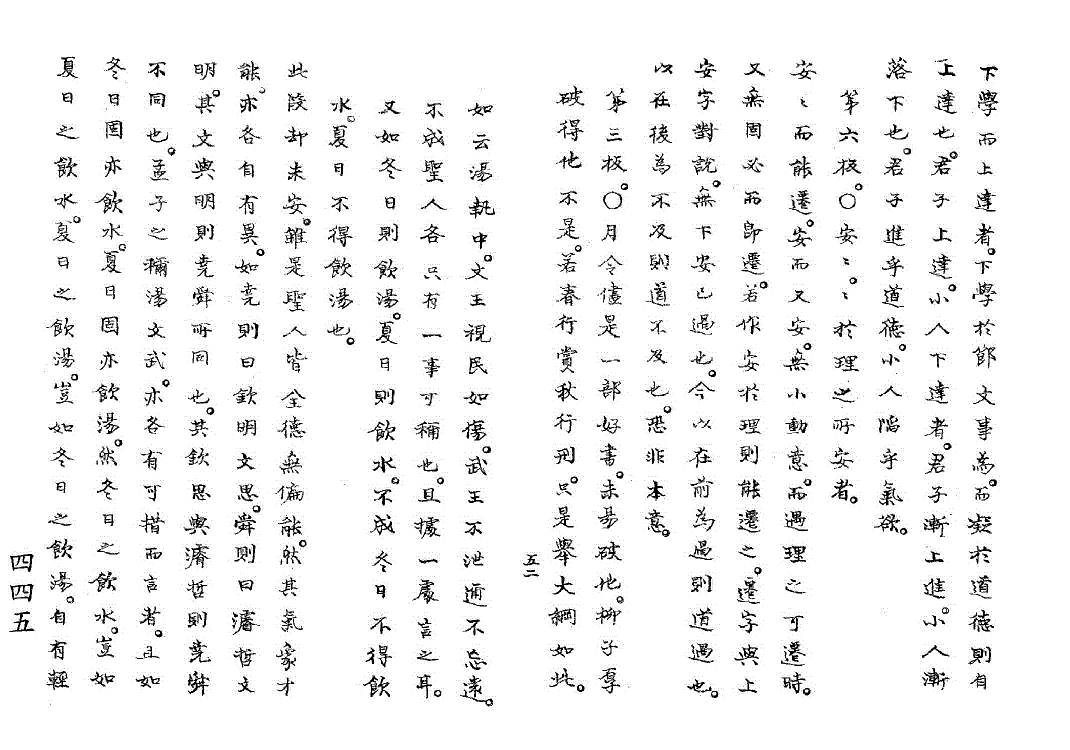 下学而上达者。下学于节文事为。而凝于道德则自上达也。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者。君子渐上进。小人渐落下也。君子进乎道德。小人陷乎气欲。
下学而上达者。下学于节文事为。而凝于道德则自上达也。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者。君子渐上进。小人渐落下也。君子进乎道德。小人陷乎气欲。第六板○安安。安于理之所安者。
安安而能迁。安而又安。无小动意。而遇理之可迁时。又无固必而即迁。若作安于理则能迁之。迁字与上安字对说。无下安已过也。今以在前为过则道过也。以在后为不及则道不及也。恐非本意。
第三板○月令尽是一部好书。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赏秋行刑。只是举大纲如此。如云汤执中。文王视民如伤。武王不泄迩不忘远。不成圣人各只有一事可称也。且据一处言之耳。又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不成冬日不得饮水。夏日不得饮汤也。
此段却未安。虽是圣人皆全德无偏能。然其气象才能。亦各自有异。如尧则曰钦明文思。舜则曰浚哲文明。其文与明则尧舜所同也。其钦思与浚哲则尧舜不同也。孟子之称汤文武。亦各有可措而言者。且如冬日固亦饮水。夏日固亦饮汤。然冬日之饮水。岂如夏日之饮水。夏日之饮汤。岂如冬日之饮汤。自有轻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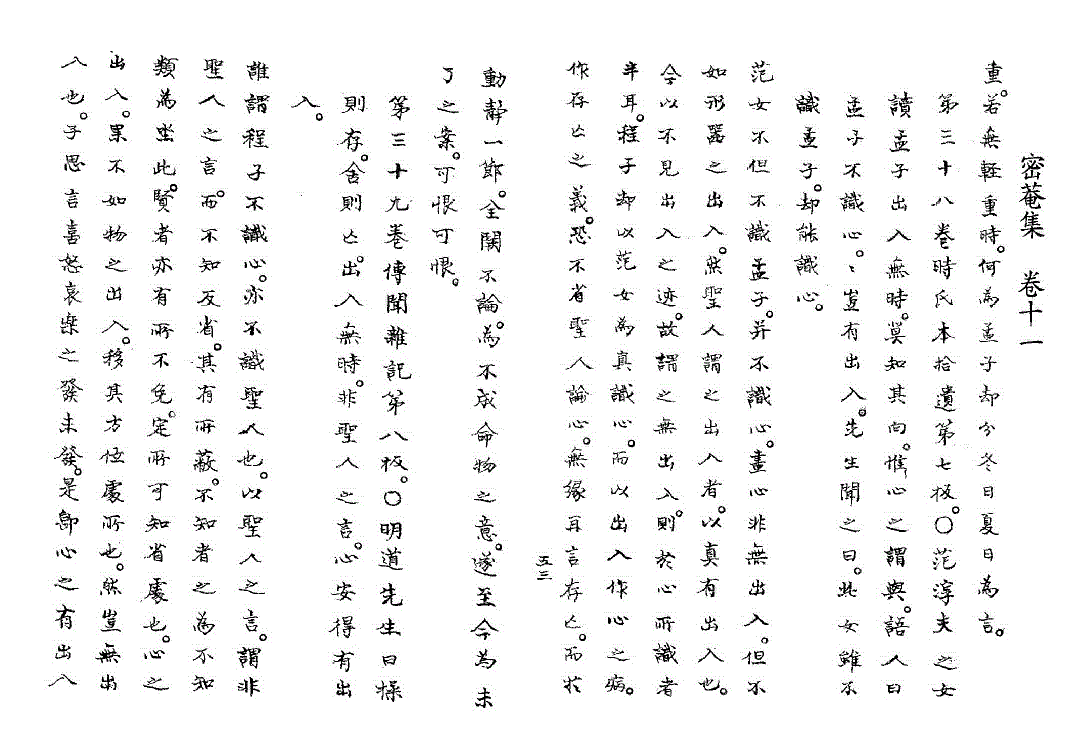 重。若无轻重时。何为孟子却分冬日夏日为言。
重。若无轻重时。何为孟子却分冬日夏日为言。第三十八卷时氏本拾遗第七板○范淳夫之女读孟子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惟心之谓与。语人曰孟子不识心。心岂有出入。先生闻之曰。此女虽不识孟子。却能识心。
范女不但不识孟子。并不识心。尽心非无出入。但不如形器之出入。然圣人谓之出入者。以真有出入也。今以不见出入之迹。故谓之无出入。则于心所识者半耳。程子却以范女为真识心。而以出入作心之病。作存亡之义。恐不省圣人论心。无缘再言存亡。而于动静一节。全阙不论。为不成命物之意。遂至今为未了之案。可恨可恨。
第三十九卷传闻杂记第八板○明道先生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非圣人之言。心安得有出入。
谁谓程子不识心。亦不识圣人也。以圣人之言。谓非圣人之言。而不知反省。其有所蔽。不知者之为不知类为坐此。贤者亦有所不免。定所可知省处也。心之出入。果不如物之出入。移其方位处所也。然岂无出入也。子思言喜怒哀乐之发未发。是即心之有出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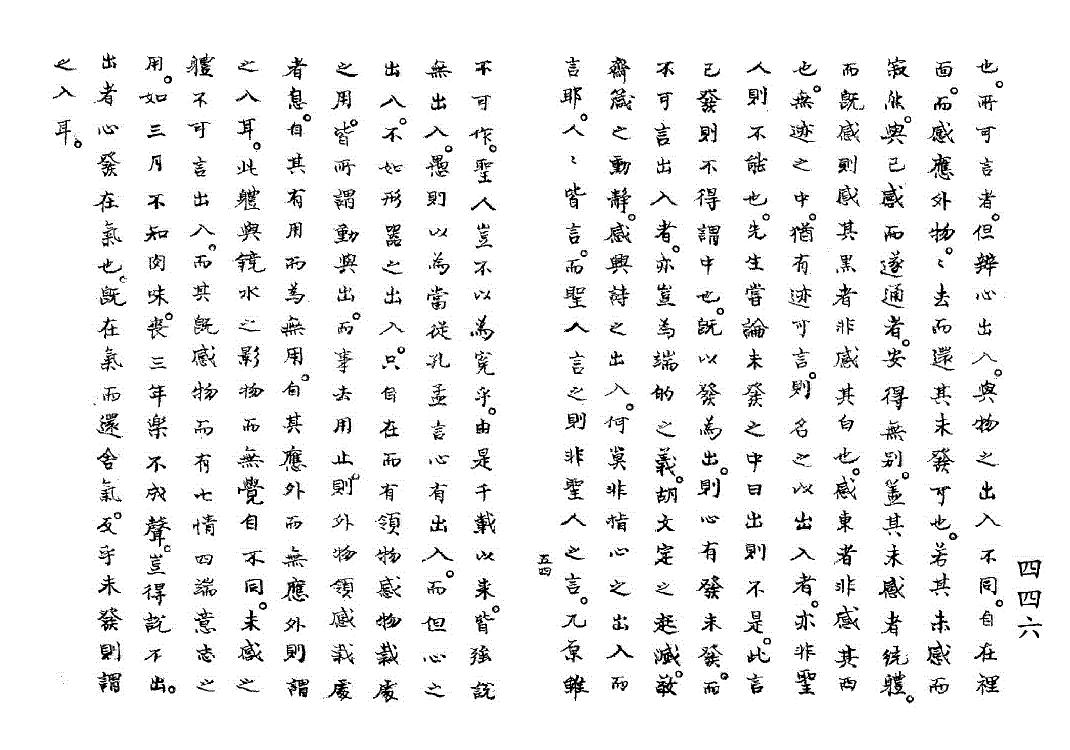 也。所可言者。但辨心出入。与物之出入不同。自在里面。而感应外物。物去而还其未发可也。若其未感而寂然。与已感而遂通者。安得无别。盖其未感者统体。而既感则感其黑者非感其白也。感东者非感其西也。无迹之中。犹有迹可言。则名之以出入者。亦非圣人则不能也。先生尝论未发之中曰出则不是。此言已发则不得谓中也。既以发为出。则心有发未发。而不可言出入者。亦岂为端的之义。胡文定之起灭。敬斋箴之动静。感兴诗之出入。何莫非指心之出入而言耶。人人皆言。而圣人言之则非圣人之言。九原虽不可作。圣人岂不以为冤乎。由是千载以来。皆强说无出入。愚则以为当从孔孟言心有出入。而但心之出入。不如形器之出入。只自在而有领物感物裁处之用。皆所谓动与出。而事去用止。则外物领感裁处者息。自其有用而为无用。自其应外而无应外则谓之入耳。此体与镜水之影物而无觉自不同。未感之体不可言出入。而其既感物而有七情四端意志之用。如三月不知肉味。丧三年乐不成声。岂得说不出。出者心发在气也。既在气而还舍气。反乎未发则谓之入耳。
也。所可言者。但辨心出入。与物之出入不同。自在里面。而感应外物。物去而还其未发可也。若其未感而寂然。与已感而遂通者。安得无别。盖其未感者统体。而既感则感其黑者非感其白也。感东者非感其西也。无迹之中。犹有迹可言。则名之以出入者。亦非圣人则不能也。先生尝论未发之中曰出则不是。此言已发则不得谓中也。既以发为出。则心有发未发。而不可言出入者。亦岂为端的之义。胡文定之起灭。敬斋箴之动静。感兴诗之出入。何莫非指心之出入而言耶。人人皆言。而圣人言之则非圣人之言。九原虽不可作。圣人岂不以为冤乎。由是千载以来。皆强说无出入。愚则以为当从孔孟言心有出入。而但心之出入。不如形器之出入。只自在而有领物感物裁处之用。皆所谓动与出。而事去用止。则外物领感裁处者息。自其有用而为无用。自其应外而无应外则谓之入耳。此体与镜水之影物而无觉自不同。未感之体不可言出入。而其既感物而有七情四端意志之用。如三月不知肉味。丧三年乐不成声。岂得说不出。出者心发在气也。既在气而还舍气。反乎未发则谓之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