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师门质疑
师门质疑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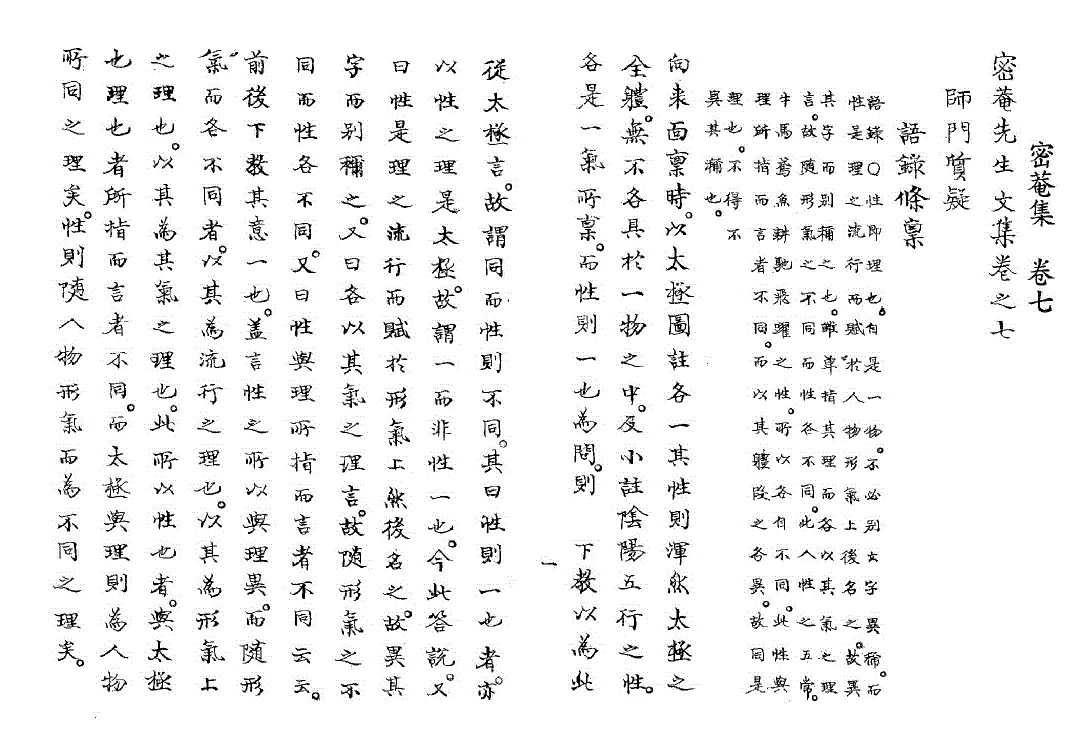 语录条禀
语录条禀(语录○性即理也。自是一物。不必别立字异称。而性是理之流行而赋于人物形气上后名之。故异其字而别称之也。虽单指其理而各以其气之理言。故随形气之不同而性各不同。此人性之五常。牛马鸢鱼耕驰飞跃之性。所以各自不同。此性与理所指而言者不同。而以其体段之各异。故同是理也。不得不异其称也。)
向来面禀时。以太极图注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及小注阴阳五行之性。各是一气所禀。而性则一也为问。则 下教以为此从太极言。故谓同而性则不同。其曰性则一也者。亦以性之理是太极。故谓一而非性一也。今此答说。又曰性是理之流行而赋于形气上然后名之。故异其字而别称之。又曰各以其气之理言。故随形气之不同而性各不同。又曰性与理所指而言者不同云云。前后下教其意一也。盖言性之所以与理异。而随形气而各不同者。以其为流行之理也。以其为形气上之理也。以其为其气之理也。此所以性也者。与太极也理也者所指而言者不同。而太极与理则为人物所同之理矣。性则随人物形气而为不同之理矣。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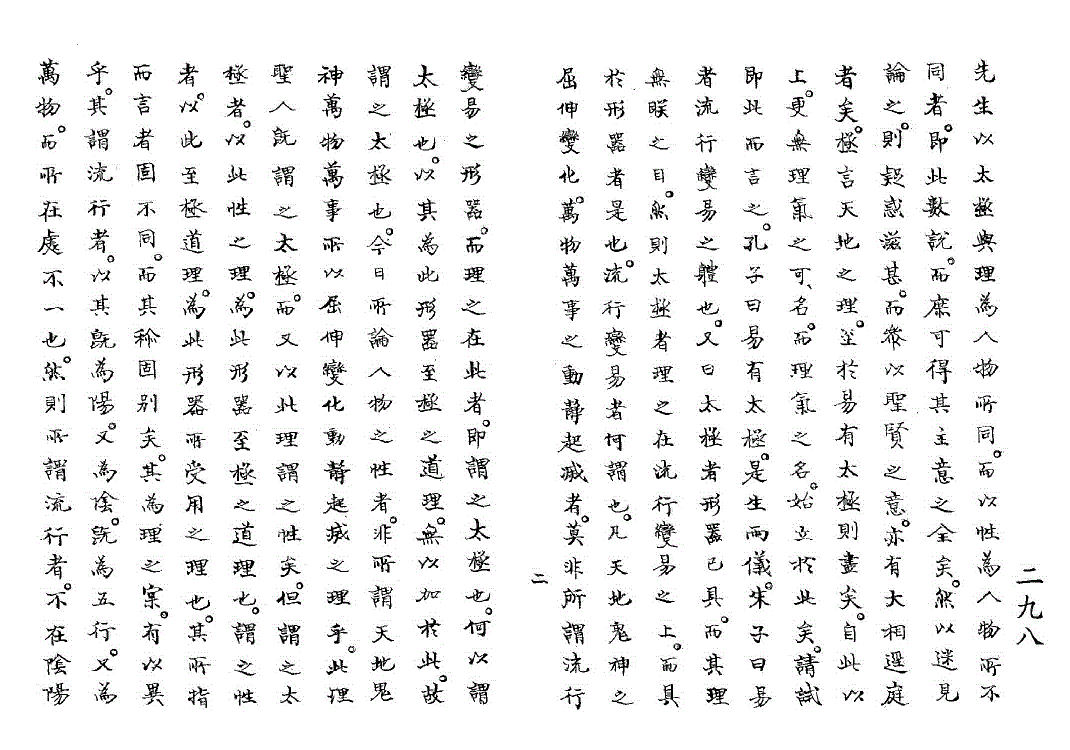 先生以太极与理为人物所同。而以性为人物所不同者。即此数说。而庶可得其主意之全矣。然以迷见论之。则疑惑滋甚。而参以圣贤之意。亦有大相径庭者矣。极言天地之理。至于易有太极则尽矣。自此以上。更无理气之可名。而理气之名。始立于此矣。请试即此而言之。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朱子曰易者流行变易之体也。又曰太极者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然则太极者理之在流行变易之上。而具于形器者是也。流行变易者何谓也。凡天地鬼神之屈伸变化。万物万事之动静起灭者。莫非所谓流行变易之形器。而理之在此者。即谓之太极也。何以谓太极也。以其为此形器至极之道理。无以加于此。故谓之太极也。今日所论人物之性者。非所谓天地鬼神万物万事所以屈伸变化动静起灭之理乎。此理圣人既谓之太极。而又以此理谓之性矣。但谓之太极者。以此性之理。为此形器至极之道理也。谓之性者。以此至极道理。为此形器所受用之理也。其所指而言者固不同。而其称固别矣。其为理之宲。有以异乎。其谓流行者。以其既为阳。又为阴。既为五行。又为万物。而所在处不一也。然则所谓流行者。不在阴阳
先生以太极与理为人物所同。而以性为人物所不同者。即此数说。而庶可得其主意之全矣。然以迷见论之。则疑惑滋甚。而参以圣贤之意。亦有大相径庭者矣。极言天地之理。至于易有太极则尽矣。自此以上。更无理气之可名。而理气之名。始立于此矣。请试即此而言之。孔子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朱子曰易者流行变易之体也。又曰太极者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之目。然则太极者理之在流行变易之上。而具于形器者是也。流行变易者何谓也。凡天地鬼神之屈伸变化。万物万事之动静起灭者。莫非所谓流行变易之形器。而理之在此者。即谓之太极也。何以谓太极也。以其为此形器至极之道理。无以加于此。故谓之太极也。今日所论人物之性者。非所谓天地鬼神万物万事所以屈伸变化动静起灭之理乎。此理圣人既谓之太极。而又以此理谓之性矣。但谓之太极者。以此性之理。为此形器至极之道理也。谓之性者。以此至极道理。为此形器所受用之理也。其所指而言者固不同。而其称固别矣。其为理之宲。有以异乎。其谓流行者。以其既为阳。又为阴。既为五行。又为万物。而所在处不一也。然则所谓流行者。不在阴阳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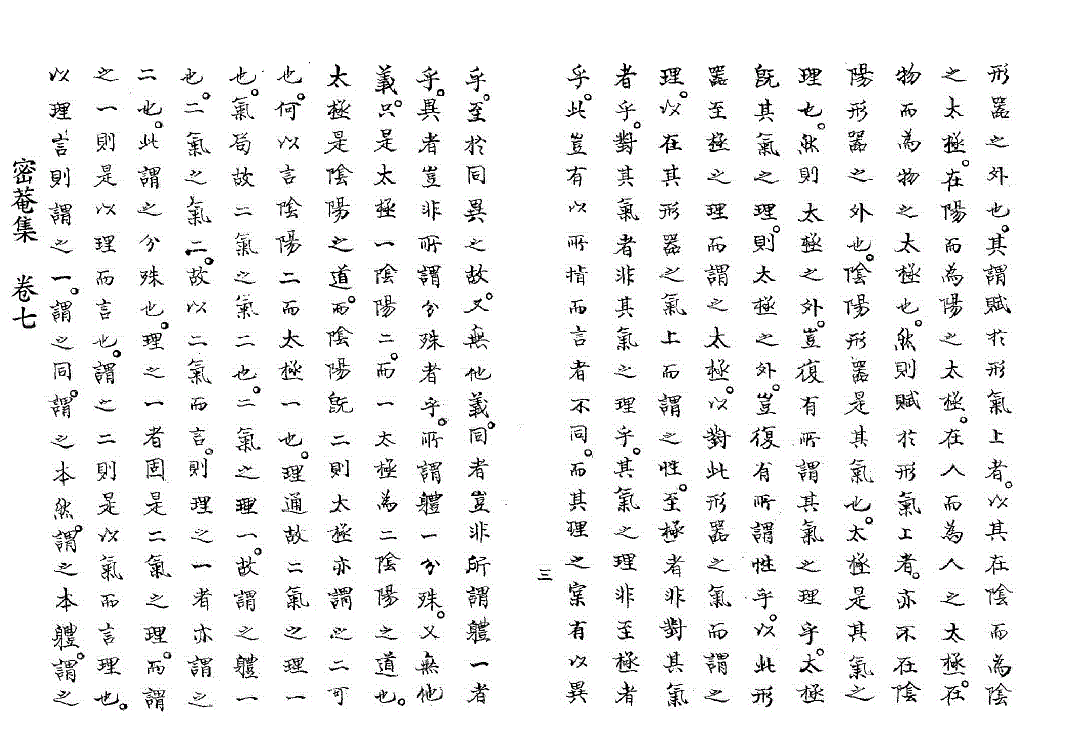 形器之外也。其谓赋于形气上者。以其在阴而为阴之太极。在阳而为阳之太极。在人而为人之太极。在物而为物之太极也。然则赋于形气上者。亦不在阴阳形器之外也。阴阳形器是其气也。太极是其气之理也。然则太极之外。岂复有所谓其气之理乎。太极既其气之理。则太极之外。岂复有所谓性乎。以此形器至极之理而谓之太极。以对此形器之气而谓之理。以在其形器之气上而谓之性。至极者非对其气者乎。对其气者非其气之理乎。其气之理非至极者乎。此岂有以所指而言者不同。而其理之宲有以异乎。至于同异之故。又无他义。同者岂非所谓体一者乎。异者岂非所谓分殊者乎。所谓体一分殊。又无他义。只是太极一阴阳二。而一太极为二阴阳之道也。太极是阴阳之道。而阴阳既二则太极亦谓之二可也。何以言阴阳二而太极一也。理通故二气之理一也。气局故二气之气二也。二气之理一。故谓之体一也。二气之气二。故以二气而言。则理之一者亦谓之二也。此谓之分殊也。理之一者固是二气之理。而谓之一则是以理而言也。谓之二则是以气而言理也。以理言则谓之一。谓之同。谓之本然。谓之本体。谓之
形器之外也。其谓赋于形气上者。以其在阴而为阴之太极。在阳而为阳之太极。在人而为人之太极。在物而为物之太极也。然则赋于形气上者。亦不在阴阳形器之外也。阴阳形器是其气也。太极是其气之理也。然则太极之外。岂复有所谓其气之理乎。太极既其气之理。则太极之外。岂复有所谓性乎。以此形器至极之理而谓之太极。以对此形器之气而谓之理。以在其形器之气上而谓之性。至极者非对其气者乎。对其气者非其气之理乎。其气之理非至极者乎。此岂有以所指而言者不同。而其理之宲有以异乎。至于同异之故。又无他义。同者岂非所谓体一者乎。异者岂非所谓分殊者乎。所谓体一分殊。又无他义。只是太极一阴阳二。而一太极为二阴阳之道也。太极是阴阳之道。而阴阳既二则太极亦谓之二可也。何以言阴阳二而太极一也。理通故二气之理一也。气局故二气之气二也。二气之理一。故谓之体一也。二气之气二。故以二气而言。则理之一者亦谓之二也。此谓之分殊也。理之一者固是二气之理。而谓之一则是以理而言也。谓之二则是以气而言理也。以理言则谓之一。谓之同。谓之本然。谓之本体。谓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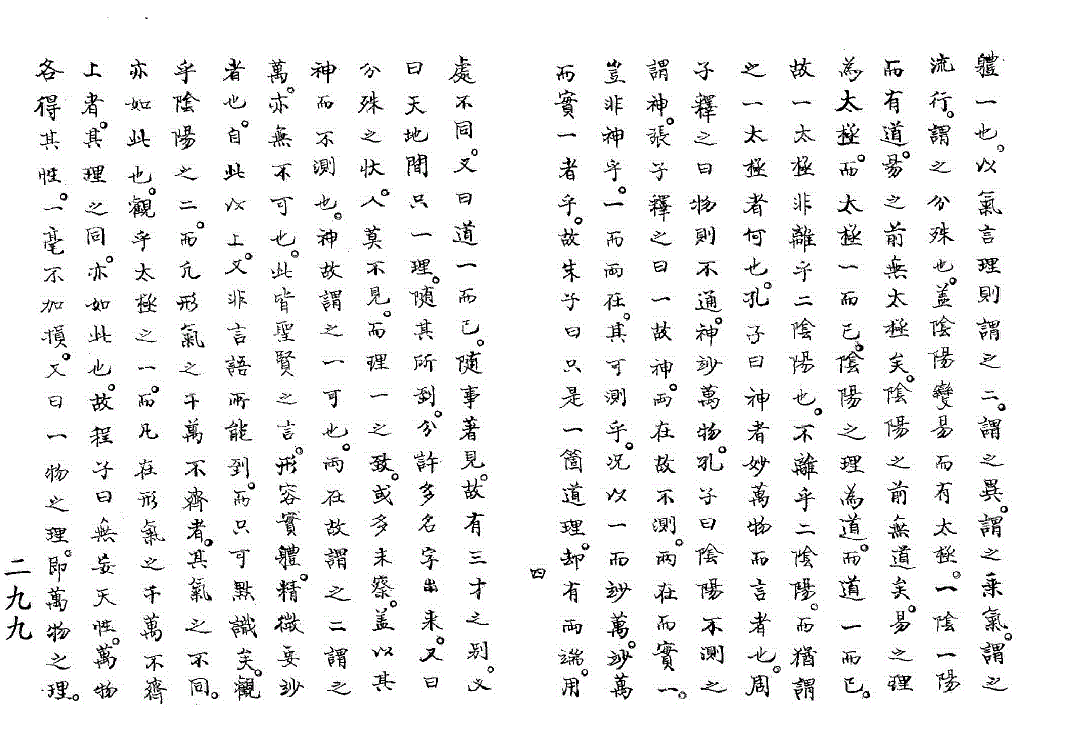 体一也。以气言理则谓之二。谓之异。谓之乘气。谓之流行。谓之分殊也。盖阴阳变易而有太极。一阴一阳而有道。易之前无太极矣。阴阳之前无道矣。易之理为太极。而太极一而已。阴阳之理为道。而道一而已。故一太极非离乎二阴阳也。不离乎二阴阳。而犹谓之一太极者何也。孔子曰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周子释之曰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孔子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张子释之曰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在而实一。岂非神乎。一而两在。其可测乎。况以一而妙万。妙万而实一者乎。故朱子曰只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用处不同。又曰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又曰天地间只一理。随其所到。分许多名字出来。又曰分殊之状。人莫不见。而理一之致。或多未察。盖以其神而不测也。神故谓之一可也。两在故谓之二谓之万。亦无不可也。此皆圣贤之言。形容实体。精微要妙者也。自此以上。又非言语所能到。而只可默识矣。观乎阴阳之二。而凡形气之千万不齐者。其气之不同。亦如此也。观乎太极之一。而凡在形气之千万不齐上者。其理之同。亦如此也。故程子曰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又曰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体一也。以气言理则谓之二。谓之异。谓之乘气。谓之流行。谓之分殊也。盖阴阳变易而有太极。一阴一阳而有道。易之前无太极矣。阴阳之前无道矣。易之理为太极。而太极一而已。阴阳之理为道。而道一而已。故一太极非离乎二阴阳也。不离乎二阴阳。而犹谓之一太极者何也。孔子曰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周子释之曰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孔子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张子释之曰一故神。两在故不测。两在而实一。岂非神乎。一而两在。其可测乎。况以一而妙万。妙万而实一者乎。故朱子曰只是一个道理。却有两端。用处不同。又曰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又曰天地间只一理。随其所到。分许多名字出来。又曰分殊之状。人莫不见。而理一之致。或多未察。盖以其神而不测也。神故谓之一可也。两在故谓之二谓之万。亦无不可也。此皆圣贤之言。形容实体。精微要妙者也。自此以上。又非言语所能到。而只可默识矣。观乎阴阳之二。而凡形气之千万不齐者。其气之不同。亦如此也。观乎太极之一。而凡在形气之千万不齐上者。其理之同。亦如此也。故程子曰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又曰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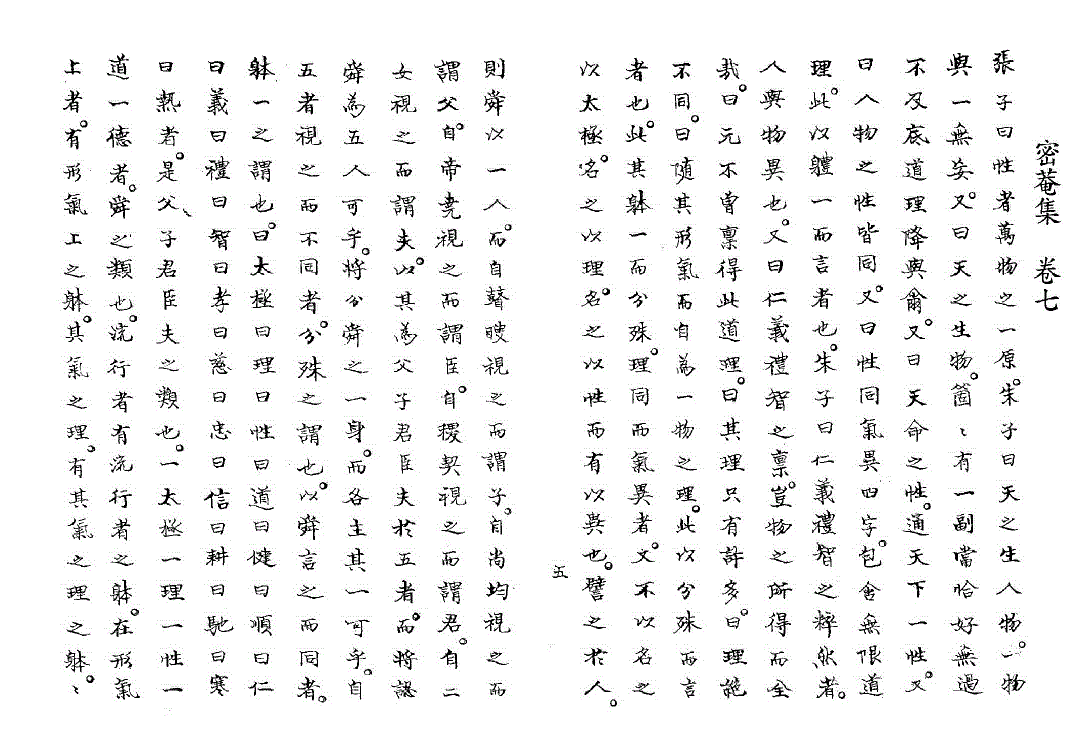 张子曰性者万物之一原。朱子曰天之生人物。一物与一无妄。又曰天之生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尔。又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又曰人物之性皆同。又曰性同气异四字。包含无限道理。此以体一而言者也。朱子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又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曰元不曾禀得此道理。曰其理只有许多。曰理绝不同。曰随其形气而自为一物之理。此以分殊而言者也。此其体一而分殊。理同而气异者。又不以名之以太极。名之以理。名之以性而有以异也。譬之于人。则舜以一人。而自瞽瞍视之而谓子。自尚均视之而谓父。自帝尧视之而谓臣。自稷契视之而谓君。自二女视之而谓夫。以其为父子君臣夫于五者。而将认舜为五人可乎。将分舜之一身。而各主其一可乎。自五者视之而不同者。分殊之谓也。以舜言之而同者。体一之谓也。曰太极曰理曰性曰道曰健曰顺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孝曰慈曰忠曰信曰耕曰驰曰寒曰热者。是父子君臣夫之类也。一太极一理一性一道一德者。舜之类也。流行者有流行者体。在形气上者。有形气上之体。其气之理。有其气之理之体。体
张子曰性者万物之一原。朱子曰天之生人物。一物与一无妄。又曰天之生物。个个有一副当恰好无过不及底道理降与尔。又曰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又曰人物之性皆同。又曰性同气异四字。包含无限道理。此以体一而言者也。朱子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又曰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曰元不曾禀得此道理。曰其理只有许多。曰理绝不同。曰随其形气而自为一物之理。此以分殊而言者也。此其体一而分殊。理同而气异者。又不以名之以太极。名之以理。名之以性而有以异也。譬之于人。则舜以一人。而自瞽瞍视之而谓子。自尚均视之而谓父。自帝尧视之而谓臣。自稷契视之而谓君。自二女视之而谓夫。以其为父子君臣夫于五者。而将认舜为五人可乎。将分舜之一身。而各主其一可乎。自五者视之而不同者。分殊之谓也。以舜言之而同者。体一之谓也。曰太极曰理曰性曰道曰健曰顺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孝曰慈曰忠曰信曰耕曰驰曰寒曰热者。是父子君臣夫之类也。一太极一理一性一道一德者。舜之类也。流行者有流行者体。在形气上者。有形气上之体。其气之理。有其气之理之体。体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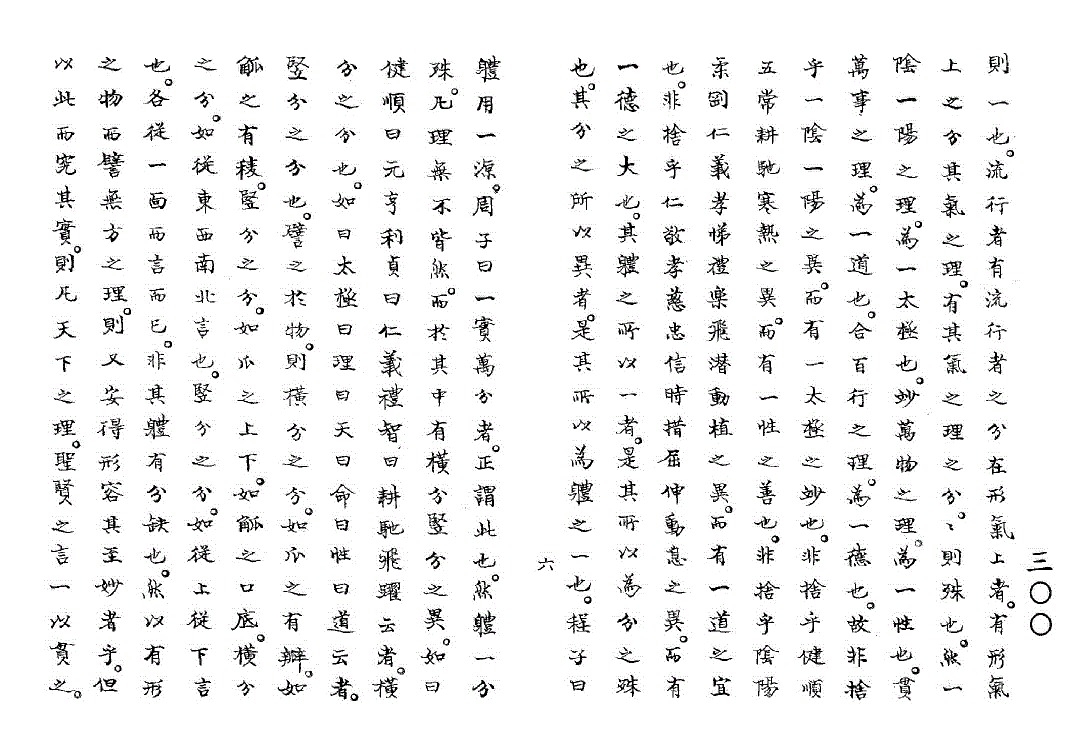 则一也。流行者有流行者之分在形气上者。有形气上之分其气之理。有其气之理之分。分则殊也。然一阴一阳之理。为一太极也。妙万物之理。为一性也。贯万事之理。为一道也。合百行之理。为一德也。故非舍乎一阴一阳之异。而有一太极之妙也。非舍乎健顺五常耕驰寒热之异。而有一性之善也。非舍乎阴阳柔刚仁义孝悌礼乐飞潜动植之异。而有一道之宜也。非舍乎仁敬孝慈忠信时措屈伸动息之异。而有一德之大也。其体之所以一者。是其所以为分之殊也。其分之所以异者。是其所以为体之一也。程子曰体用一源。周子曰一实万分者。正谓此也。然体一分殊。凡理无不皆然。而于其中有横分竖分之异。如曰健顺曰元亨利贞曰仁义礼智曰耕驰飞跃云者。横分之分也。如曰太极曰理曰天曰命曰性曰道云者。竖分之分也。譬之于物。则横分之分。如瓜之有瓣。如觚之有棱。竖分之分。如瓜之上下。如觚之口底。横分之分。如从东西南北言也。竖分之分。如从上从下言也。各从一面而言而已。非其体有分缺也。然以有形之物而譬无方之理。则又安得形容其至妙者乎。但以此而究其实。则凡天下之理。圣贤之言一以贯之。
则一也。流行者有流行者之分在形气上者。有形气上之分其气之理。有其气之理之分。分则殊也。然一阴一阳之理。为一太极也。妙万物之理。为一性也。贯万事之理。为一道也。合百行之理。为一德也。故非舍乎一阴一阳之异。而有一太极之妙也。非舍乎健顺五常耕驰寒热之异。而有一性之善也。非舍乎阴阳柔刚仁义孝悌礼乐飞潜动植之异。而有一道之宜也。非舍乎仁敬孝慈忠信时措屈伸动息之异。而有一德之大也。其体之所以一者。是其所以为分之殊也。其分之所以异者。是其所以为体之一也。程子曰体用一源。周子曰一实万分者。正谓此也。然体一分殊。凡理无不皆然。而于其中有横分竖分之异。如曰健顺曰元亨利贞曰仁义礼智曰耕驰飞跃云者。横分之分也。如曰太极曰理曰天曰命曰性曰道云者。竖分之分也。譬之于物。则横分之分。如瓜之有瓣。如觚之有棱。竖分之分。如瓜之上下。如觚之口底。横分之分。如从东西南北言也。竖分之分。如从上从下言也。各从一面而言而已。非其体有分缺也。然以有形之物而譬无方之理。则又安得形容其至妙者乎。但以此而究其实。则凡天下之理。圣贤之言一以贯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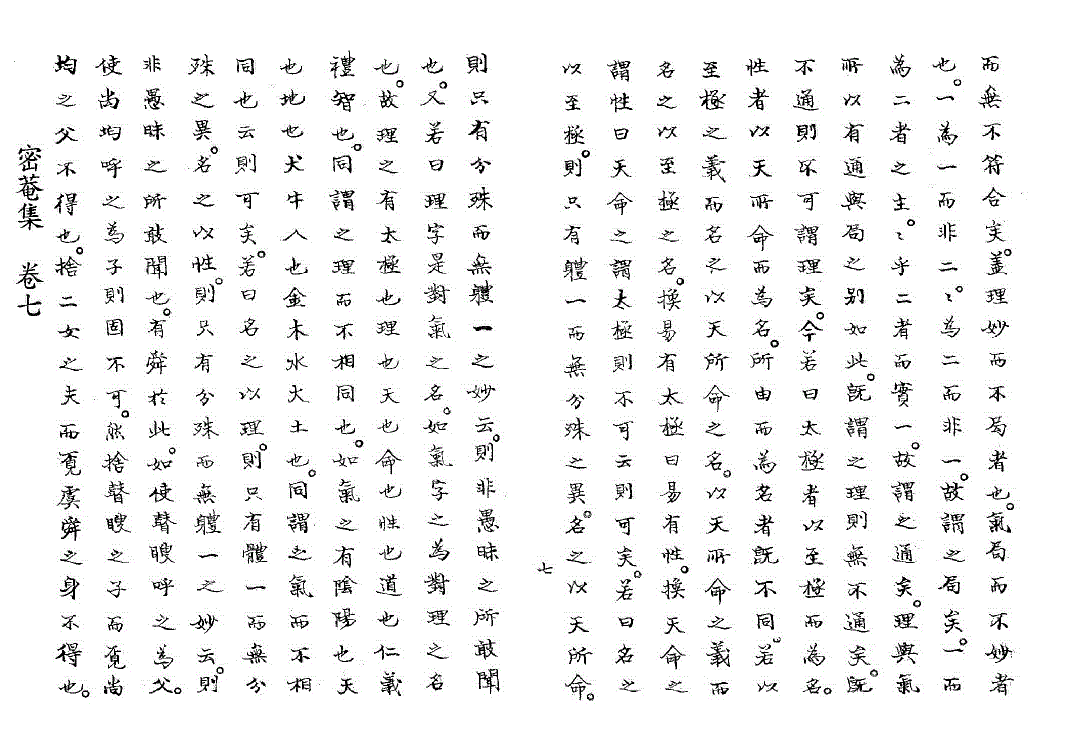 而无不符合矣。盖理妙而不局者也。气局而不妙者也。一为一而非二。二为二而非一。故谓之局矣。一而为二者之主。主乎二者而实一。故谓之通矣。理与气所以有通与局之别如此。既谓之理则无不通矣。既不通则不可谓理矣。今若曰太极者以至极而为名。性者以天所命而为名。所由而为名者既不同。若以至极之义而名之以天所命之名。以天所命之义而名之以至极之名。换易有太极曰易有性。换天命之谓性曰天命之谓太极则不可云则可矣。若曰名之以至极。则只有体一而无分殊之异。名之以天所命。则只有分殊而无体一之妙云。则非愚昧之所敢闻也。又若曰理字是对气之名。如气字之为对理之名也。故理之有太极也理也天也命也性也道也仁义礼智也。同谓之理而不相同也。如气之有阴阳也天也地也犬牛人也金木水火土也。同谓之气而不相同也云则可矣。若曰名之以理。则只有体一而无分殊之异。名之以性。则只有分殊而无体一之妙云。则非愚昧之所敢闻也。有舜于此。如使瞽瞍呼之为父。使尚均呼之为子则固不可。然舍瞽瞍之子而觅尚均之父不得也。舍二女之夫而觅虞舜之身不得也。
而无不符合矣。盖理妙而不局者也。气局而不妙者也。一为一而非二。二为二而非一。故谓之局矣。一而为二者之主。主乎二者而实一。故谓之通矣。理与气所以有通与局之别如此。既谓之理则无不通矣。既不通则不可谓理矣。今若曰太极者以至极而为名。性者以天所命而为名。所由而为名者既不同。若以至极之义而名之以天所命之名。以天所命之义而名之以至极之名。换易有太极曰易有性。换天命之谓性曰天命之谓太极则不可云则可矣。若曰名之以至极。则只有体一而无分殊之异。名之以天所命。则只有分殊而无体一之妙云。则非愚昧之所敢闻也。又若曰理字是对气之名。如气字之为对理之名也。故理之有太极也理也天也命也性也道也仁义礼智也。同谓之理而不相同也。如气之有阴阳也天也地也犬牛人也金木水火土也。同谓之气而不相同也云则可矣。若曰名之以理。则只有体一而无分殊之异。名之以性。则只有分殊而无体一之妙云。则非愚昧之所敢闻也。有舜于此。如使瞽瞍呼之为父。使尚均呼之为子则固不可。然舍瞽瞍之子而觅尚均之父不得也。舍二女之夫而觅虞舜之身不得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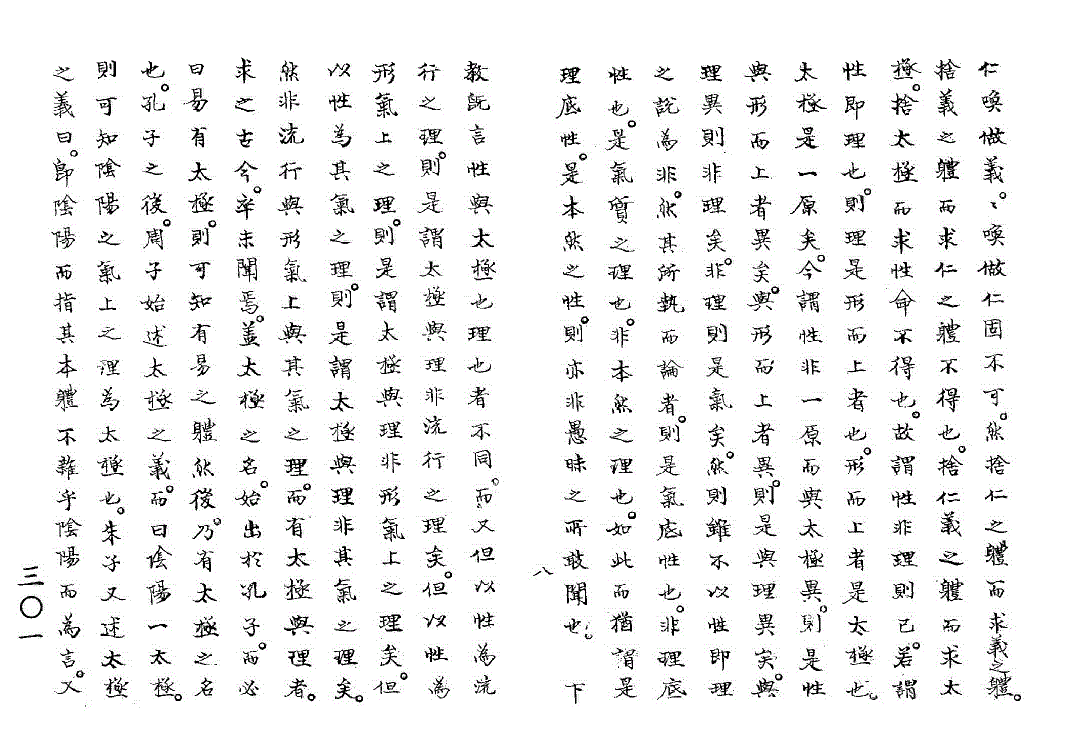 仁唤做义。义唤做仁固不可。然舍仁之体而求义之体。舍义之体而求仁之体不得也。舍仁义之体而求太极。舍太极而求性命不得也。故谓性非理则已。若谓性即理也。则理是形而上者也。形而上者是太极也。太极是一原矣。今谓性非一原而与太极异。则是性与形而上者异矣。与形而上者异。则是与理异矣。与理异则非理矣。非理则是气矣。然则虽不以性即理之说为非。然其所执而论者。则是气底性也。非理底性也。是气质之理也。非本然之理也。如此而犹谓是理底性。是本然之性。则亦非愚昧之所敢闻也。 下教既言性与太极也理也者不同。而又但以性为流行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流行之理矣。但以性为形气上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形气上之理矣。但以性为其气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其气之理矣。然非流行与形气上与其气之理。而有太极与理者。求之古今。卒未闻焉。盖太极之名。始出于孔子。而必曰易有太极。则可知有易之体然后。乃有太极之名也。孔子之后。周子始述太极之义。而曰阴阳一太极。则可知阴阳之气上之理为太极也。朱子又述太极之义曰。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又
仁唤做义。义唤做仁固不可。然舍仁之体而求义之体。舍义之体而求仁之体不得也。舍仁义之体而求太极。舍太极而求性命不得也。故谓性非理则已。若谓性即理也。则理是形而上者也。形而上者是太极也。太极是一原矣。今谓性非一原而与太极异。则是性与形而上者异矣。与形而上者异。则是与理异矣。与理异则非理矣。非理则是气矣。然则虽不以性即理之说为非。然其所执而论者。则是气底性也。非理底性也。是气质之理也。非本然之理也。如此而犹谓是理底性。是本然之性。则亦非愚昧之所敢闻也。 下教既言性与太极也理也者不同。而又但以性为流行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流行之理矣。但以性为形气上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形气上之理矣。但以性为其气之理。则是谓太极与理非其气之理矣。然非流行与形气上与其气之理。而有太极与理者。求之古今。卒未闻焉。盖太极之名。始出于孔子。而必曰易有太极。则可知有易之体然后。乃有太极之名也。孔子之后。周子始述太极之义。而曰阴阳一太极。则可知阴阳之气上之理为太极也。朱子又述太极之义曰。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又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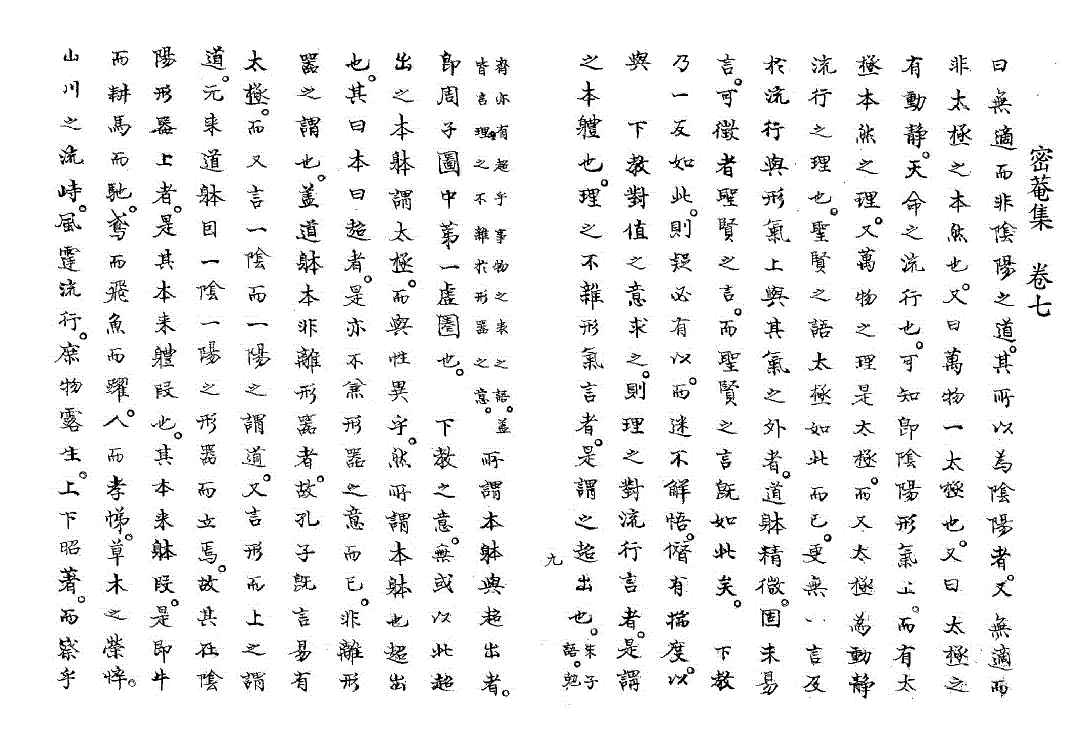 曰无适而非阴阳之道。其所以为阴阳者。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又曰万物一太极也。又曰太极之有动静。天命之流行也。可知即阴阳形气上。而有太极本然之理。又万物之理是太极。而又太极为动静流行之理也。圣贤之语太极如此而已。更无一言及于流行与形气上与其气之外者。道体精微。固未易言。可徵者圣贤之言。而圣贤之言既如此矣。 下教乃一反如此。则疑必有以。而迷不解悟。僭有揣度。以与 下教对值之意求之。则理之对流行言者。是谓之本体也。理之不杂形气言者。是谓之超出也。(朱子语。勉齐亦有超乎事物之表之语。盖皆言理之不杂于形器之意。)所谓本体与超出者。即周子图中第一虚圈也。 下教之意。无或以此超出之本体谓太极。而与性异乎。然所谓本体也超出也。其曰本曰超者。是亦不兼形器之意而已。非离形器之谓也。盖道体本非离形器者。故孔子既言易有太极。而又言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言形而上之谓道。元来道体因一阴一阳之形器而立焉。故其在阴阳形器上者。是其本来体段也。其本来体段。是即牛而耕马而驰。鸢而飞鱼而跃。人而孝悌。草木之荣悴。山川之流峙。风霆流行。庶物露生。上下昭著。而察乎
曰无适而非阴阳之道。其所以为阴阳者。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又曰万物一太极也。又曰太极之有动静。天命之流行也。可知即阴阳形气上。而有太极本然之理。又万物之理是太极。而又太极为动静流行之理也。圣贤之语太极如此而已。更无一言及于流行与形气上与其气之外者。道体精微。固未易言。可徵者圣贤之言。而圣贤之言既如此矣。 下教乃一反如此。则疑必有以。而迷不解悟。僭有揣度。以与 下教对值之意求之。则理之对流行言者。是谓之本体也。理之不杂形气言者。是谓之超出也。(朱子语。勉齐亦有超乎事物之表之语。盖皆言理之不杂于形器之意。)所谓本体与超出者。即周子图中第一虚圈也。 下教之意。无或以此超出之本体谓太极。而与性异乎。然所谓本体也超出也。其曰本曰超者。是亦不兼形器之意而已。非离形器之谓也。盖道体本非离形器者。故孔子既言易有太极。而又言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言形而上之谓道。元来道体因一阴一阳之形器而立焉。故其在阴阳形器上者。是其本来体段也。其本来体段。是即牛而耕马而驰。鸢而飞鱼而跃。人而孝悌。草木之荣悴。山川之流峙。风霆流行。庶物露生。上下昭著。而察乎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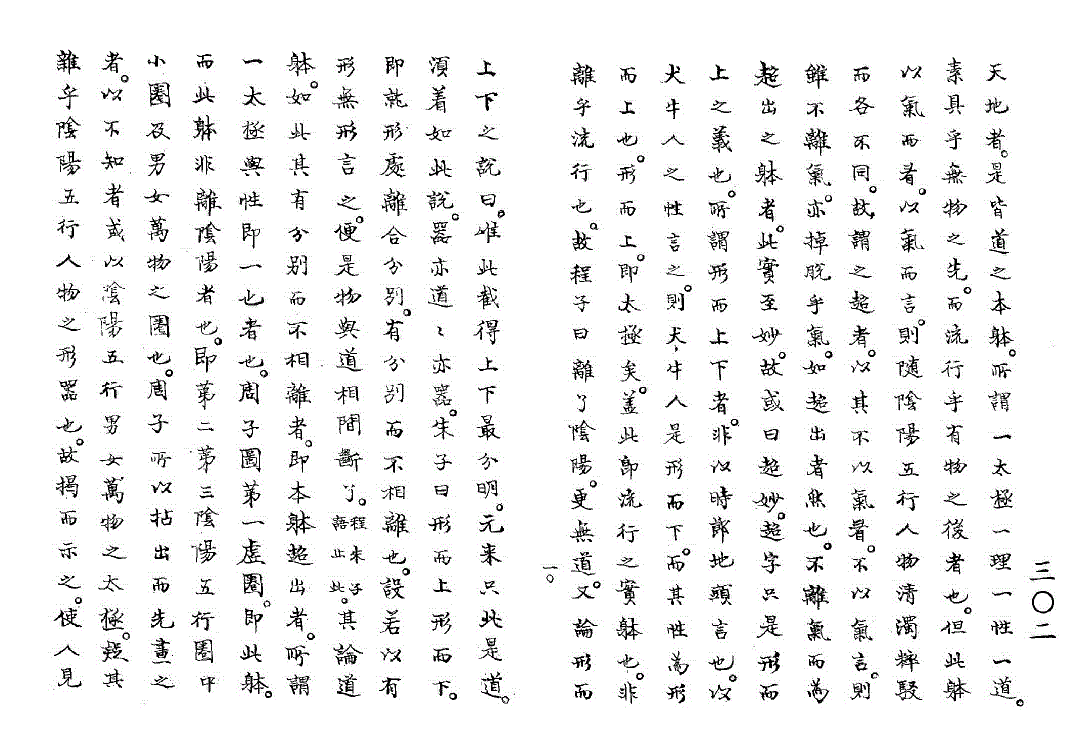 天地者。是皆道之本体。所谓一太极一理一性一道。素具乎无物之先。而流行乎有物之后者也。但此体以气而看。以气而言。则随阴阳五行人物清浊粹驳而各不同。故谓之超者。以其不以气看。不以气言。则虽不离气。亦掉脱乎气。如超出者然也。不离气而为超出之体者。此实至妙。故或曰超妙。超字只是形而上之义也。所谓形而上下者。非以时节地头言也。以犬牛人之性言之。则犬牛人是形而下。而其性为形而上也。形而上。即太极矣。盖此即流行之实体也。非离乎流行也。故程子曰离了阴阳。更无道。又论形而上下之说曰。唯此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朱子曰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有分别而不相离也。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道相间断了。(程朱子语止此。)其论道体。如此其有分别而不相离者。即本体超出者。所谓一太极与性即一也者也。周子图第一虚圈。即此体。而此体非离阴阳者也。即第二第三阴阳五行圈中小圈及男女万物之圈也。周子所以拈出而先画之者。以不知者或以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之太极。疑其杂乎阴阳五行人物之形器也。故揭而示之。使人见
天地者。是皆道之本体。所谓一太极一理一性一道。素具乎无物之先。而流行乎有物之后者也。但此体以气而看。以气而言。则随阴阳五行人物清浊粹驳而各不同。故谓之超者。以其不以气看。不以气言。则虽不离气。亦掉脱乎气。如超出者然也。不离气而为超出之体者。此实至妙。故或曰超妙。超字只是形而上之义也。所谓形而上下者。非以时节地头言也。以犬牛人之性言之。则犬牛人是形而下。而其性为形而上也。形而上。即太极矣。盖此即流行之实体也。非离乎流行也。故程子曰离了阴阳。更无道。又论形而上下之说曰。唯此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朱子曰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有分别而不相离也。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道相间断了。(程朱子语止此。)其论道体。如此其有分别而不相离者。即本体超出者。所谓一太极与性即一也者也。周子图第一虚圈。即此体。而此体非离阴阳者也。即第二第三阴阳五行圈中小圈及男女万物之圈也。周子所以拈出而先画之者。以不知者或以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之太极。疑其杂乎阴阳五行人物之形器也。故揭而示之。使人见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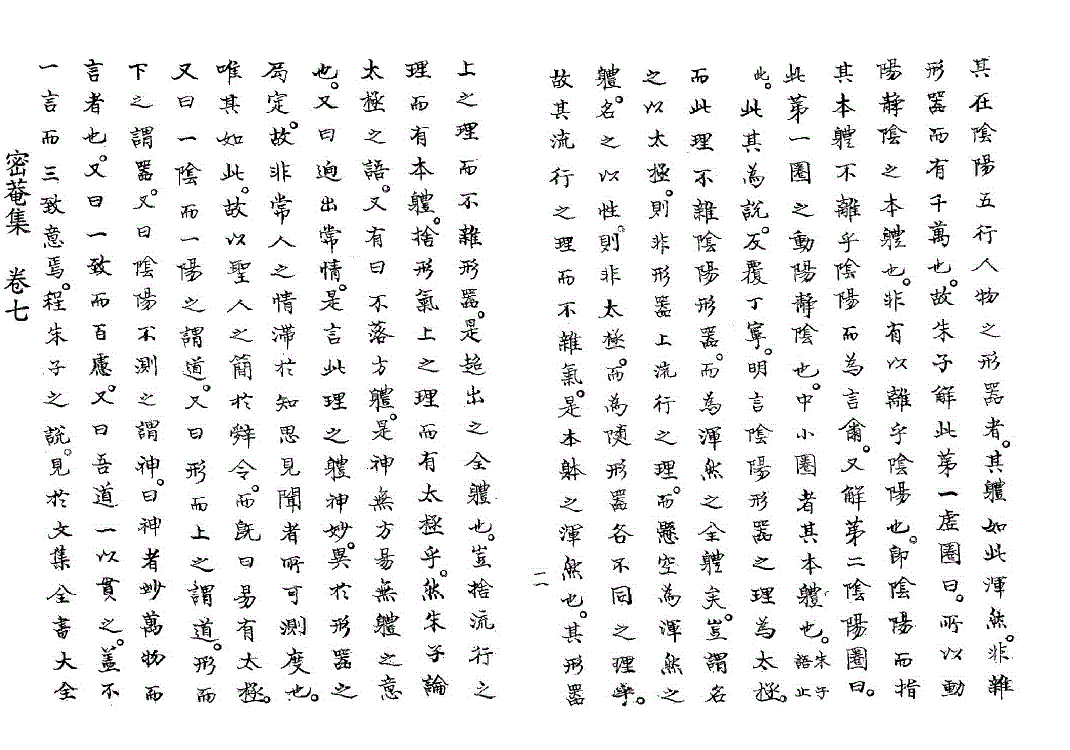 其在阴阳五行人物之形器者。其体如此浑然。非杂形器而有千万也。故朱子解此第一虚圈曰。所以动阳静阴之本体也。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离乎阴阳而为言尔。又解第二阴阳圈曰。此第一圈之动阳静阴也。中小圈者其本体也。(朱子语止此。)此其为说。反覆丁宁。明言阴阳形器之理为太极。而此理不杂阴阳形器。而为浑然之全体矣。岂谓名之以太极。则非形器上流行之理。而悬空为浑然之体。名之以性。则非太极。而为随形器各不同之理乎。故其流行之理而不杂气。是本体之浑然也。其形器上之理而不杂形器。是超出之全体也。岂舍流行之理而有本体。舍形气上之理而有太极乎。然朱子论太极之语。又有曰不落方体。是神无方易无体之意也。又曰迥出常情。是言此理之体神妙。异于形器之局定。故非常人之情滞于知思见闻者所可测度也。唯其如此。故以圣人之简于辞令。而既曰易有太极。又曰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曰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又曰一致而百虑。又曰吾道一以贯之。盖不一言而三致意焉。程朱子之说。见于文集全书大全
其在阴阳五行人物之形器者。其体如此浑然。非杂形器而有千万也。故朱子解此第一虚圈曰。所以动阳静阴之本体也。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离乎阴阳而为言尔。又解第二阴阳圈曰。此第一圈之动阳静阴也。中小圈者其本体也。(朱子语止此。)此其为说。反覆丁宁。明言阴阳形器之理为太极。而此理不杂阴阳形器。而为浑然之全体矣。岂谓名之以太极。则非形器上流行之理。而悬空为浑然之体。名之以性。则非太极。而为随形器各不同之理乎。故其流行之理而不杂气。是本体之浑然也。其形器上之理而不杂形器。是超出之全体也。岂舍流行之理而有本体。舍形气上之理而有太极乎。然朱子论太极之语。又有曰不落方体。是神无方易无体之意也。又曰迥出常情。是言此理之体神妙。异于形器之局定。故非常人之情滞于知思见闻者所可测度也。唯其如此。故以圣人之简于辞令。而既曰易有太极。又曰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曰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曰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又曰一致而百虑。又曰吾道一以贯之。盖不一言而三致意焉。程朱子之说。见于文集全书大全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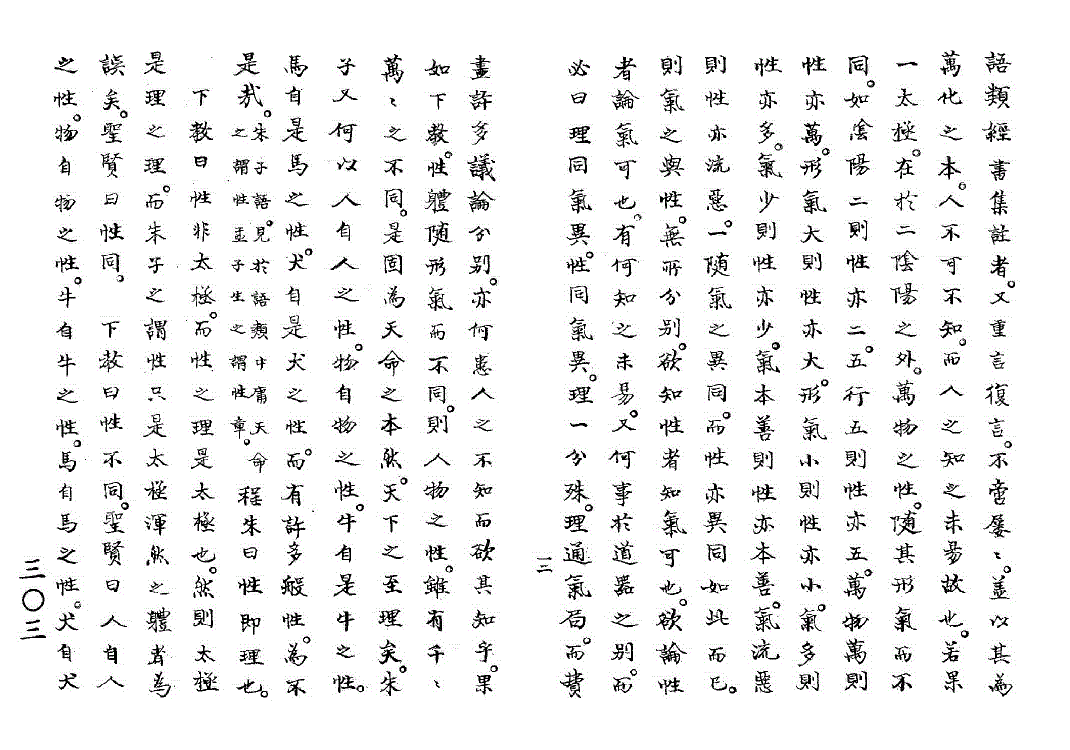 语类经书集注者。又重言复言。不啻屡屡。盖以其为万化之本。人不可不知。而人之知之未易故也。若果一太极。在于二阴阳之外。万物之性。随其形气而不同。如阴阳二则性亦二。五行五则性亦五。万物万则性亦万。形气大则性亦大。形气小则性亦小。气多则性亦多。气少则性亦少。气本善则性亦本善。气流恶则性亦流恶。一随气之异同。而性亦异同如此而已。则气之与性。无所分别。欲知性者知气可也。欲论性者论气可也。有何知之未易。又何事于道器之别。而必曰理同气异。性同气异。理一分殊。理通气局。而费尽许多议论分别。亦何患人之不知而欲其知乎。果如下教。性体随形气而不同。则人物之性。虽有千千万万之不同。是固为天命之本然。天下之至理矣。朱子又何以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牛自是牛之性。马自是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而有许多般性。为不是哉。(朱子语。见于语类中庸天命之谓性孟子生之谓性章。)程朱曰性即理也。 下教曰性非太极。而性之理是太极也。然则太极是理之理。而朱子之谓性只是太极浑然之体者为误矣。圣贤曰性同。 下教曰性不同。圣贤曰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牛自牛之性。马自马之性。犬自犬
语类经书集注者。又重言复言。不啻屡屡。盖以其为万化之本。人不可不知。而人之知之未易故也。若果一太极。在于二阴阳之外。万物之性。随其形气而不同。如阴阳二则性亦二。五行五则性亦五。万物万则性亦万。形气大则性亦大。形气小则性亦小。气多则性亦多。气少则性亦少。气本善则性亦本善。气流恶则性亦流恶。一随气之异同。而性亦异同如此而已。则气之与性。无所分别。欲知性者知气可也。欲论性者论气可也。有何知之未易。又何事于道器之别。而必曰理同气异。性同气异。理一分殊。理通气局。而费尽许多议论分别。亦何患人之不知而欲其知乎。果如下教。性体随形气而不同。则人物之性。虽有千千万万之不同。是固为天命之本然。天下之至理矣。朱子又何以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牛自是牛之性。马自是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而有许多般性。为不是哉。(朱子语。见于语类中庸天命之谓性孟子生之谓性章。)程朱曰性即理也。 下教曰性非太极。而性之理是太极也。然则太极是理之理。而朱子之谓性只是太极浑然之体者为误矣。圣贤曰性同。 下教曰性不同。圣贤曰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牛自牛之性。马自马之性。犬自犬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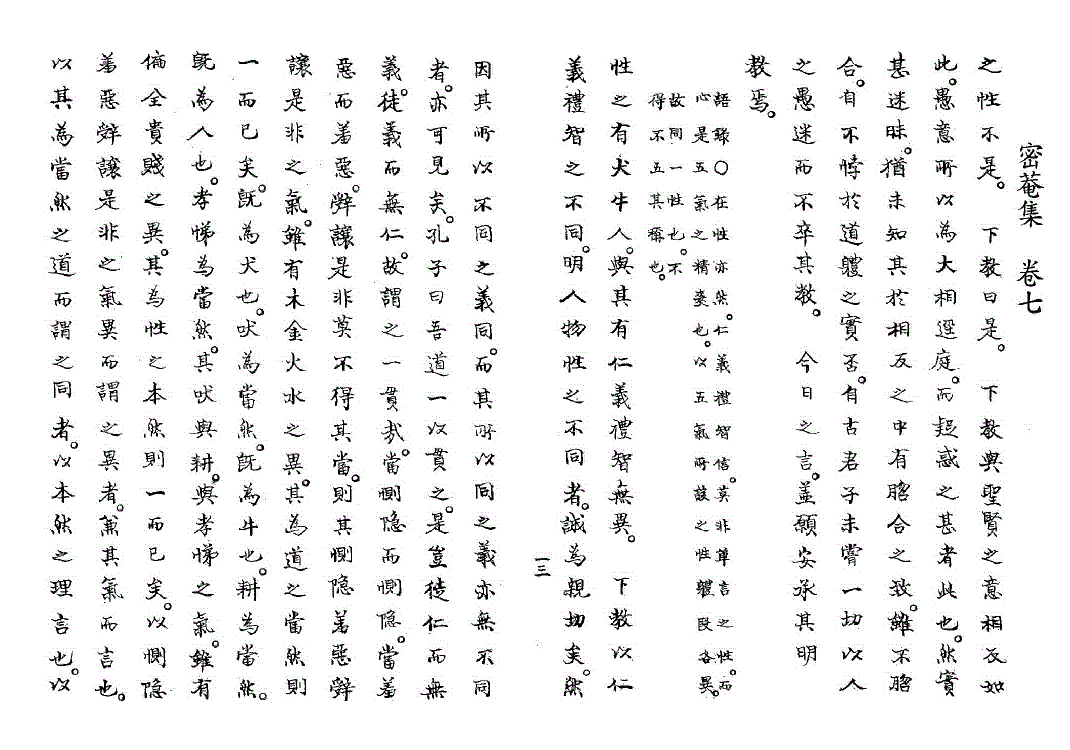 之性不是。 下教曰是。 下教与圣贤之意相反如此。愚意所以为大相径庭。而疑惑之甚者此也。然实甚迷昧。犹未知其于相反之中有吻合之致。虽不吻合。自不悖于道体之实否。自古君子未尝一切以人之愚迷而不卒其教。 今日之言。盖愿安承其明 教焉。
之性不是。 下教曰是。 下教与圣贤之意相反如此。愚意所以为大相径庭。而疑惑之甚者此也。然实甚迷昧。犹未知其于相反之中有吻合之致。虽不吻合。自不悖于道体之实否。自古君子未尝一切以人之愚迷而不卒其教。 今日之言。盖愿安承其明 教焉。(语录○在性亦然。仁义礼智信。莫非单言之性。而心是五气之精爽也。以五气所该之性体段各异。故同一性也。不得不五其称也。)
性之有犬牛人。与其有仁义礼智无异。 下教以仁义礼智之不同。明人物性之不同者。诚为亲切矣。然因其所以不同之义同。而其所以同之义亦无不同者。亦可见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是岂徒仁而无义。徒义而无仁。故谓之一贯哉。当恻隐而恻隐。当羞恶而羞恶。辞让是非莫不得其当。则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虽有木金火水之异。其为道之当然则一而已矣。既为犬也。吠为当然。既为牛也。耕为当然。既为人也。孝悌为当然。其吠与耕。与孝悌之气。虽有偏全贵贱之异。其为性之本然则一而已矣。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气异而谓之异者。兼其气而言也。以其为当然之道而谓之同者。以本然之理言也。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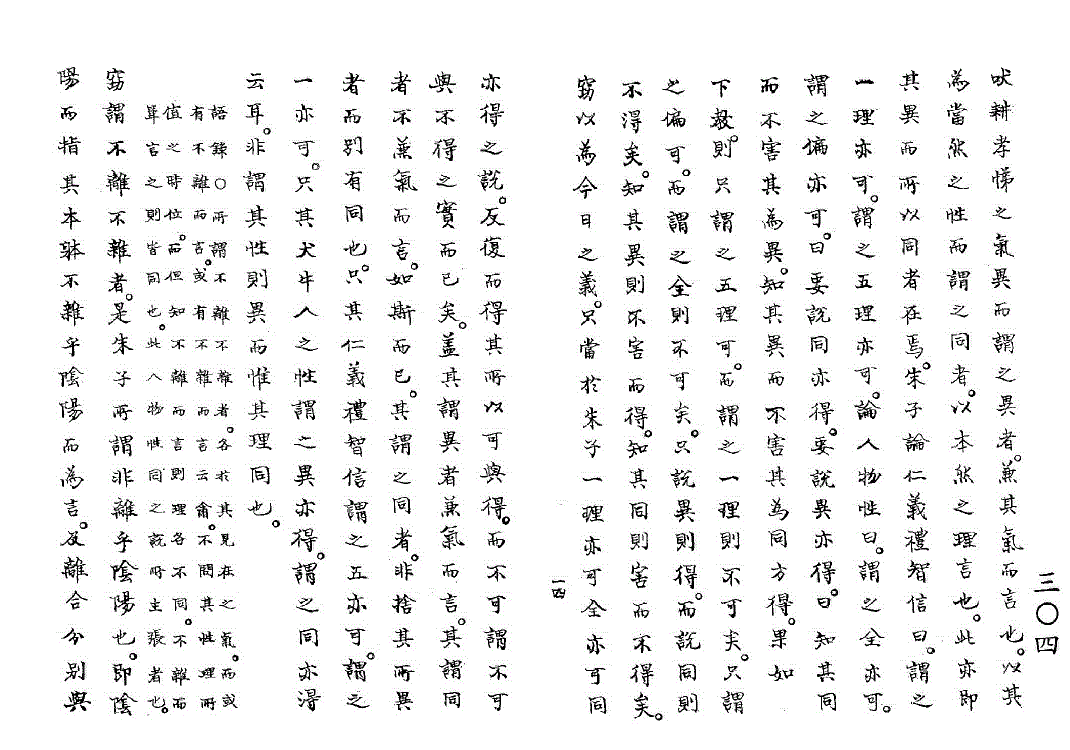 吠耕孝悌之气异而谓之异者。兼其气而言也。以其为当然之性而谓之同者。以本然之理言也。此亦即其异而所以同者在焉。朱子论仁义礼智信曰。谓之一理亦可。谓之五理亦可。论人物性曰。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曰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曰知其同而不害其为异。知其异而不害其为同方得。果如 下教。则只谓之五理可。而谓之一理则不可矣。只谓之偏可。而谓之全则不可矣。只说异则得。而说同则不得矣。知其异则不害而得。知其同则害而不得矣。窃以为今日之义。只当于朱子一理亦可全亦可同亦得之说。反复而得其所以可与得。而不可谓不可与不得之实而已矣。盖其谓异者兼气而言。其谓同者不兼气而言。如斯而已。其谓之同者。非舍其所异者而别有同也。只其仁义礼智信谓之五亦可。谓之一亦可。只其犬牛人之性谓之异亦得。谓之同亦得云耳。非谓其性则异而惟其理同也。
吠耕孝悌之气异而谓之异者。兼其气而言也。以其为当然之性而谓之同者。以本然之理言也。此亦即其异而所以同者在焉。朱子论仁义礼智信曰。谓之一理亦可。谓之五理亦可。论人物性曰。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曰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曰知其同而不害其为异。知其异而不害其为同方得。果如 下教。则只谓之五理可。而谓之一理则不可矣。只谓之偏可。而谓之全则不可矣。只说异则得。而说同则不得矣。知其异则不害而得。知其同则害而不得矣。窃以为今日之义。只当于朱子一理亦可全亦可同亦得之说。反复而得其所以可与得。而不可谓不可与不得之实而已矣。盖其谓异者兼气而言。其谓同者不兼气而言。如斯而已。其谓之同者。非舍其所异者而别有同也。只其仁义礼智信谓之五亦可。谓之一亦可。只其犬牛人之性谓之异亦得。谓之同亦得云耳。非谓其性则异而惟其理同也。(语录○所谓不离不杂者。各于其见在之气。而或有不离而言。或有不杂而言云尔。不问其性理所值之时位。而但知不离而言则理各不同。不杂而单言之则皆同也。此人物性同之说所主张者也。)
窃谓不离不杂者。是朱子所谓非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及离合分别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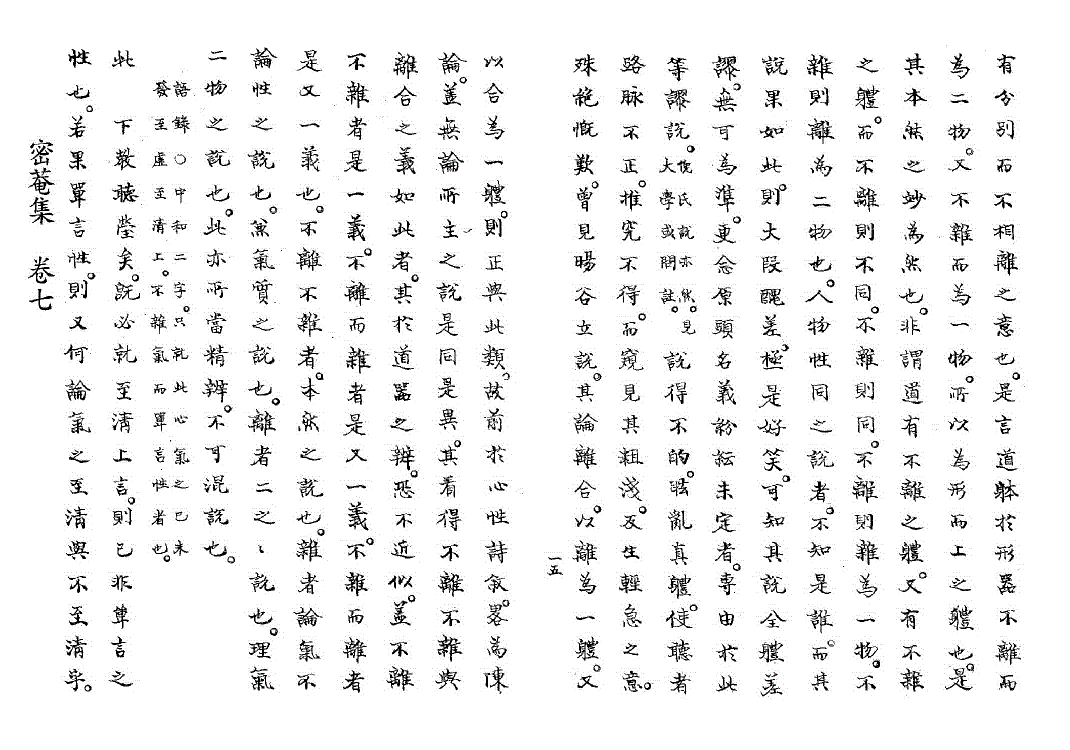 有分别而不相离之意也。是言道体于形器不离而为二物。又不杂而为一物。所以为形而上之体也。是其本然之妙为然也。非谓道有不离之体。又有不杂之体。而不离则不同。不杂则同。不离则杂为一物。不杂则离为二物也。人物性同之说者。不知是谁。而其说果如此。则大段丑差。极是好笑。可知其说全体差谬。无可为准。更念原头名义纷纭未定者。专由于此等谬说。(傀氏说亦然。见大学或问注。)说得不的。眩乱真体。使听者路脉不正。推究不得。而窥见其粗浅。反生轻急之意。殊绝慨叹。曾见旸谷立说。其论离合。以离为一体。又以合为一体。则正与此类。故前于心性诗叙。略为陈论。盖无论所主之说是同是异。其看得不离不杂与离合之义如此者。其于道器之辨。恐不近似。盖不离不杂者是一义。不离而杂者是又一义。不杂而离者是又一义也。不离不杂者。本然之说也。杂者论气不论性之说也。兼气质之说也。离者二之之说也。理气二物之说也。此亦所当精辨。不可混说也。
有分别而不相离之意也。是言道体于形器不离而为二物。又不杂而为一物。所以为形而上之体也。是其本然之妙为然也。非谓道有不离之体。又有不杂之体。而不离则不同。不杂则同。不离则杂为一物。不杂则离为二物也。人物性同之说者。不知是谁。而其说果如此。则大段丑差。极是好笑。可知其说全体差谬。无可为准。更念原头名义纷纭未定者。专由于此等谬说。(傀氏说亦然。见大学或问注。)说得不的。眩乱真体。使听者路脉不正。推究不得。而窥见其粗浅。反生轻急之意。殊绝慨叹。曾见旸谷立说。其论离合。以离为一体。又以合为一体。则正与此类。故前于心性诗叙。略为陈论。盖无论所主之说是同是异。其看得不离不杂与离合之义如此者。其于道器之辨。恐不近似。盖不离不杂者是一义。不离而杂者是又一义。不杂而离者是又一义也。不离不杂者。本然之说也。杂者论气不论性之说也。兼气质之说也。离者二之之说也。理气二物之说也。此亦所当精辨。不可混说也。(语录○中和二字。只就此心气之已未发至虚至清上。不杂气而单言性者也。)
此 下教听莹矣。既必就至清上言。则已非单言之性也。若果单言性。则又何论气之至清与不至清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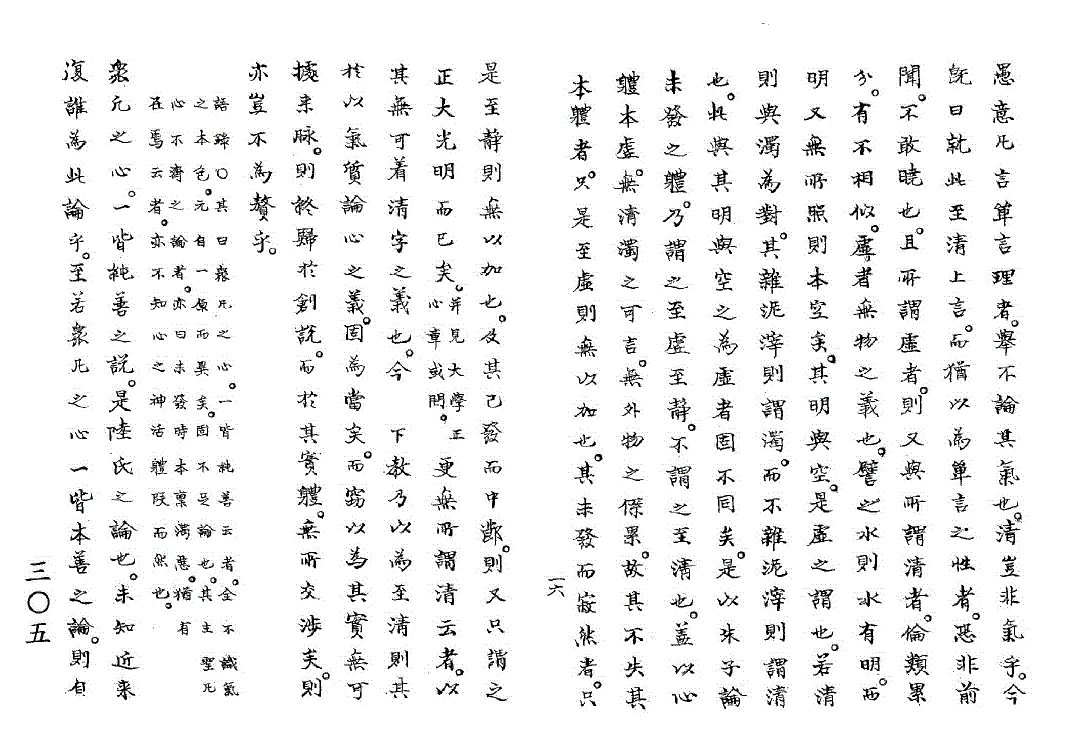 愚意凡言单言理者。举不论其气也。清岂非气乎。今既曰就此至清上言。而犹以为单言之性者。恐非前闻。不敢晓也。且所谓虚者。则又与所谓清者。伦类累分。有不相似。虚者无物之义也。譬之水则水有明。而明又无所照则本空矣。其明与空。是虚之谓也。若清则与浊为对。其杂泥滓则谓浊。而不杂泥滓则谓清也。此与其明与空之为虚者固不同矣。是以朱子论未发之体。乃谓之至虚至静。不谓之至清也。盖以心体本虚。无清浊之可言。无外物之系累。故其不失其本体者。只是至虚则无以加也。其未发而寂然者。只是至静则无以加也。及其已发而中节。则又只谓之正大光明而已矣。(并见大学正心章或问。)更无所谓清云者。以其无可着清字之义也。今 下教乃以为至清则其于以气质论心之义。固为当矣。而窃以为其实无可据来脉。则终归于创说。而于其实体。无所交涉矣。则亦岂不为赘乎。
愚意凡言单言理者。举不论其气也。清岂非气乎。今既曰就此至清上言。而犹以为单言之性者。恐非前闻。不敢晓也。且所谓虚者。则又与所谓清者。伦类累分。有不相似。虚者无物之义也。譬之水则水有明。而明又无所照则本空矣。其明与空。是虚之谓也。若清则与浊为对。其杂泥滓则谓浊。而不杂泥滓则谓清也。此与其明与空之为虚者固不同矣。是以朱子论未发之体。乃谓之至虚至静。不谓之至清也。盖以心体本虚。无清浊之可言。无外物之系累。故其不失其本体者。只是至虚则无以加也。其未发而寂然者。只是至静则无以加也。及其已发而中节。则又只谓之正大光明而已矣。(并见大学正心章或问。)更无所谓清云者。以其无可着清字之义也。今 下教乃以为至清则其于以气质论心之义。固为当矣。而窃以为其实无可据来脉。则终归于创说。而于其实体。无所交涉矣。则亦岂不为赘乎。(语录○其曰众凡之心。一皆纯善云者。全不识气之本色。元自一原而异矣。固不足论也。其主圣凡心不齐之论者。亦曰未发时本禀浊恶。犹有在焉云者。亦不知心之神活体段而然也。)
众凡之心。一皆纯善之说。是陆氏之论也。未知近来复谁为此论乎。至若众凡之心一皆本善之论。则自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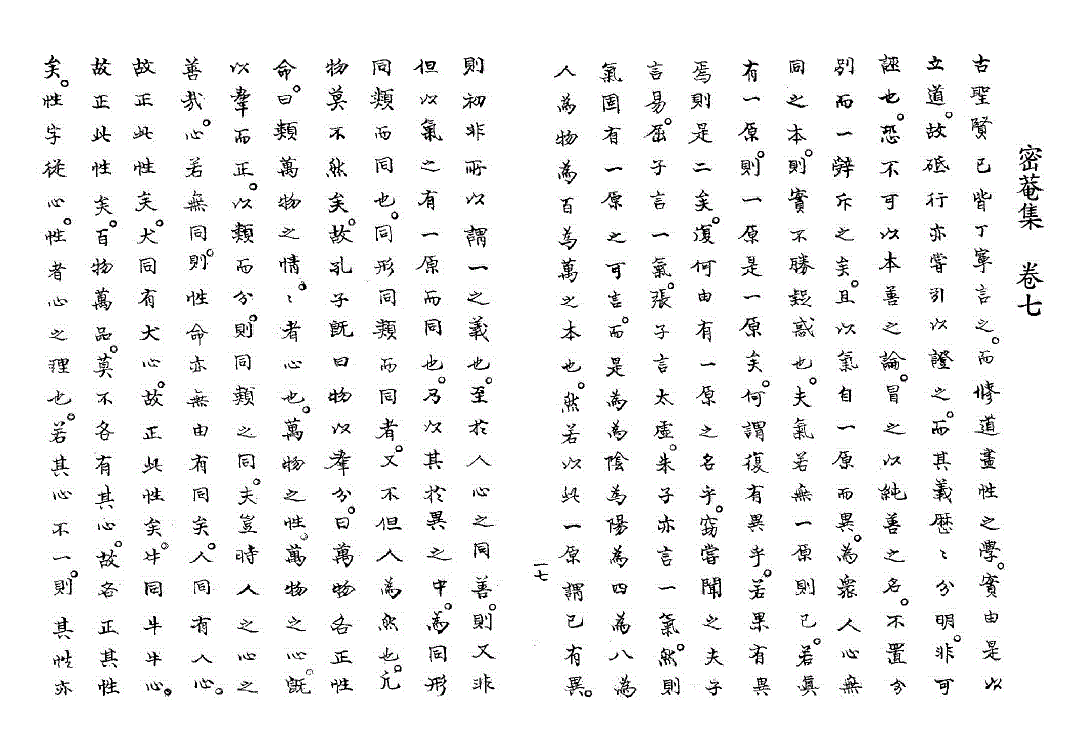 古圣贤已皆丁宁言之。而修道尽性之学。实由是以立道。故砥行亦尝引以證之。而其义历历分明。非可诬也。恐不可以本善之论。冒之以纯善之名。不置分别而一辞斥之矣。且以气自一原而异。为众人心无同之本。则实不胜疑惑也。夫气若无一原则已。若真有一原。则一原是一原矣。何谓复有异乎。若果有异焉则是二矣。复何由有一原之名乎。窃尝闻之夫子言易。屈子言一气。张子言太虚。朱子亦言一气。然则气固有一原之可言。而是为为阴为阳为四为八为人为物为百为万之本也。然若以此一原谓已有异。则初非所以谓一之义也。至于人心之同善。则又非但以气之有一原而同也。乃以其于异之中。为同形同类而同也。同形同类而同者。又不但人为然也。凡物莫不然矣。故孔子既曰物以群分。曰万物各正性命。曰类万物之情。情者心也。万物之性。万物之心。既以群而正。以类而分。则同类之同。夫岂时人之心之善哉。心若无同。则性命亦无由有同矣。人同有人心。故正此性矣。犬同有犬心。故正此性矣。牛同牛牛心。故正此性矣。百物万品。莫不各有其心。故各正其性矣。性字从心。性者心之理也。若其心不一。则其性亦
古圣贤已皆丁宁言之。而修道尽性之学。实由是以立道。故砥行亦尝引以證之。而其义历历分明。非可诬也。恐不可以本善之论。冒之以纯善之名。不置分别而一辞斥之矣。且以气自一原而异。为众人心无同之本。则实不胜疑惑也。夫气若无一原则已。若真有一原。则一原是一原矣。何谓复有异乎。若果有异焉则是二矣。复何由有一原之名乎。窃尝闻之夫子言易。屈子言一气。张子言太虚。朱子亦言一气。然则气固有一原之可言。而是为为阴为阳为四为八为人为物为百为万之本也。然若以此一原谓已有异。则初非所以谓一之义也。至于人心之同善。则又非但以气之有一原而同也。乃以其于异之中。为同形同类而同也。同形同类而同者。又不但人为然也。凡物莫不然矣。故孔子既曰物以群分。曰万物各正性命。曰类万物之情。情者心也。万物之性。万物之心。既以群而正。以类而分。则同类之同。夫岂时人之心之善哉。心若无同。则性命亦无由有同矣。人同有人心。故正此性矣。犬同有犬心。故正此性矣。牛同牛牛心。故正此性矣。百物万品。莫不各有其心。故各正其性矣。性字从心。性者心之理也。若其心不一。则其性亦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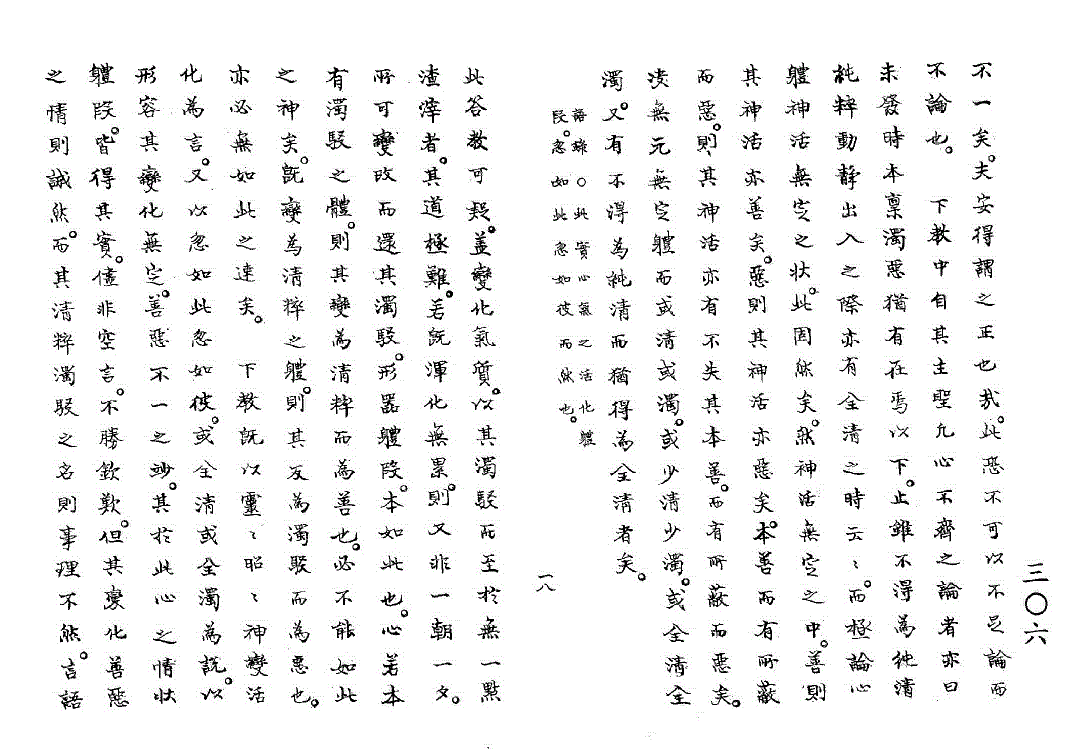 不一矣。夫安得谓之正也哉。此恐不可以不足论而不论也。 下教中自其主圣凡心不齐之论者亦曰未发时本禀浊恶犹有在焉以下。止虽不得为纯清纯粹动静出入之际亦有全清之时云云。而极论心体神活无定之状。此固然矣。然神活无定之中。善则其神活亦善矣。恶则其神活亦恶矣。本善而有所蔽而恶。则其神活亦有不失其本善。而有所蔽而恶矣。决无元无定体而或清或浊。或少清少浊。或全清全浊。又有不得为纯清而犹得为全清者矣。
不一矣。夫安得谓之正也哉。此恐不可以不足论而不论也。 下教中自其主圣凡心不齐之论者亦曰未发时本禀浊恶犹有在焉以下。止虽不得为纯清纯粹动静出入之际亦有全清之时云云。而极论心体神活无定之状。此固然矣。然神活无定之中。善则其神活亦善矣。恶则其神活亦恶矣。本善而有所蔽而恶。则其神活亦有不失其本善。而有所蔽而恶矣。决无元无定体而或清或浊。或少清少浊。或全清全浊。又有不得为纯清而犹得为全清者矣。(语录○此实心气之活化体段。忽如此忽如彼而然也。)
此答教可疑。盖变化气质。以其浊驳而至于无一点渣滓者。其道极难。若既浑化无累。则又非一朝一夕。所可变改而还其浊驳。形器体段。本如此也。心若本有浊驳之体。则其变为清粹而为善也。必不能如此之神矣。既变为清粹之体。则其反为浊驳而为恶也。亦必无如此之速矣。 下教既以灵灵昭昭神变活化为言。又以忽如此忽如彼。或全清或全浊为说。以形容其变化无定。善恶不一之妙。其于此心之情状体段。皆得其实。尽非空言。不胜钦叹。但其变化善恶之情则诚然。而其清粹浊驳之名则事理不然。言语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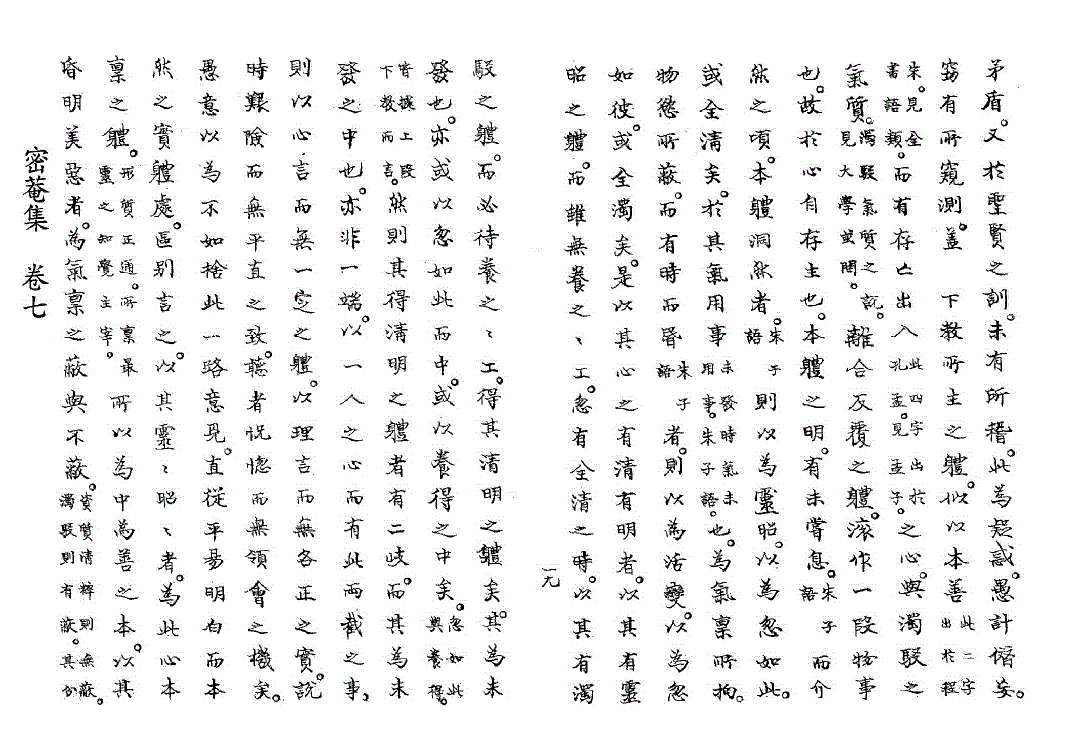 矛盾。又于圣贤之训。未有所稽。此为疑惑。愚计僭妄。窃有所窥测。盖 下教所主之体。似以本善(此二字出于程朱。见全书语类。)而有存亡出入(此四字出于孔孟。见孟子。)之心。与浊驳之气质。(浊驳气质之说。见大学或问。)离合反覆之体。滚作一段物事也。故于心自存主也。本体之明。有未尝息。(朱子语)而介然之顷。本体洞然者。(朱子语)则以为灵昭。以为忽如此。或全清矣。于其气用事(未发时气未用事。朱子语。)也。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有时而昏(朱子语)者。则以为活变。以为忽如彼。或全浊矣。是以其心之有清有明者。以其有灵昭之体。而虽无养之之工。忽有全清之时。以其有浊驳之体。而必待养之之工。得其清明之体矣。其为未发也。亦或以忽如此而中。或以养得之中矣。(忽如此与养得。皆据上段下教而言。)然则其得清明之体者有二岐。而其为未发之中也。亦非一端。以一人之心而有此两截之事。则以心言而无一定之体。以理言而无各正之实。说时艰险而无平直之致。听者恍惚而无领会之机矣。愚意以为不如舍此一路意见。直从平易明白而本然之实体处。区别言之。以其灵灵昭昭者。为此心本禀之体。(形质正通。所禀最灵之知觉主宰。)所以为中为善之本。以其昏明美恶者。为气禀之蔽与不蔽。(资质清粹则无蔽。浊驳则有蔽。其分
矛盾。又于圣贤之训。未有所稽。此为疑惑。愚计僭妄。窃有所窥测。盖 下教所主之体。似以本善(此二字出于程朱。见全书语类。)而有存亡出入(此四字出于孔孟。见孟子。)之心。与浊驳之气质。(浊驳气质之说。见大学或问。)离合反覆之体。滚作一段物事也。故于心自存主也。本体之明。有未尝息。(朱子语)而介然之顷。本体洞然者。(朱子语)则以为灵昭。以为忽如此。或全清矣。于其气用事(未发时气未用事。朱子语。)也。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而有时而昏(朱子语)者。则以为活变。以为忽如彼。或全浊矣。是以其心之有清有明者。以其有灵昭之体。而虽无养之之工。忽有全清之时。以其有浊驳之体。而必待养之之工。得其清明之体矣。其为未发也。亦或以忽如此而中。或以养得之中矣。(忽如此与养得。皆据上段下教而言。)然则其得清明之体者有二岐。而其为未发之中也。亦非一端。以一人之心而有此两截之事。则以心言而无一定之体。以理言而无各正之实。说时艰险而无平直之致。听者恍惚而无领会之机矣。愚意以为不如舍此一路意见。直从平易明白而本然之实体处。区别言之。以其灵灵昭昭者。为此心本禀之体。(形质正通。所禀最灵之知觉主宰。)所以为中为善之本。以其昏明美恶者。为气禀之蔽与不蔽。(资质清粹则无蔽。浊驳则有蔽。其分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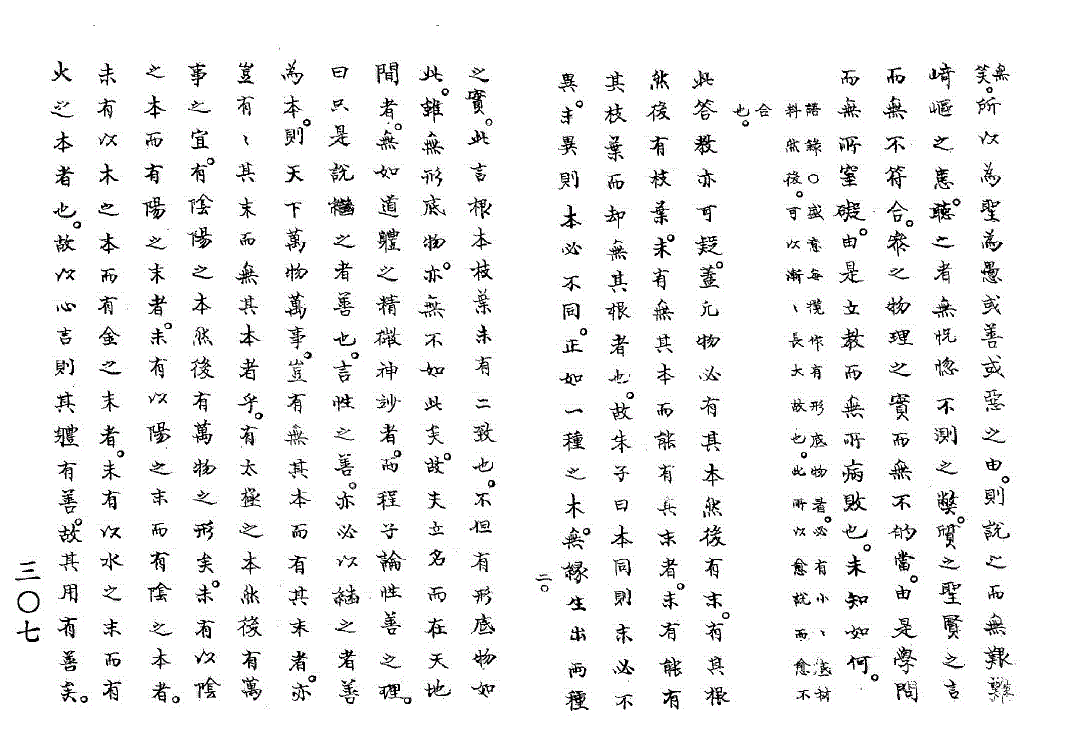 无笑。)所以为圣为愚或善或恶之由。则说之而无艰难崎岖之患。听之者无恍惚不测之弊。质之圣贤之言而无不符合。参之物理之实而无不的当。由是学问而无所窒碍。由是立教而无所病败也。未知如何。
无笑。)所以为圣为愚或善或恶之由。则说之而无艰难崎岖之患。听之者无恍惚不测之弊。质之圣贤之言而无不符合。参之物理之实而无不的当。由是学问而无所窒碍。由是立教而无所病败也。未知如何。(语录○盛意每揽作有形底物看。必有小小底材料然后。可以渐渐长大故也。此所以愈说而愈不合也。)
此答教亦可疑。盖凡物必有其本然后有末。有其根然后有枝叶。未有无其本而能有其末者。未有能有其枝叶而却无其根者也。故朱子曰本同则末必不异。末异则本必不同。正如一种之木。无缘生出两种之实。此言根本枝叶未有二致也。不但有形底物如此。虽无形底物。亦无不如此矣。故夫立名而在天地间者。无如道体之精微神妙者。而程子论性善之理。曰只是说继之者善也。言性之善。亦必以继之者善为本。则天下万物万事。岂有无其本而有其末者。亦岂有有其末而无其本者乎。有太极之本然后有万事之宜。有阴阳之本然后有万物之形矣。未有以阴之本而有阳之末者。未有以阳之末而有阴之本者。未有以木之本而有金之末者。未有以水之末而有火之本者也。故以心言则其体有善。故其用有善矣。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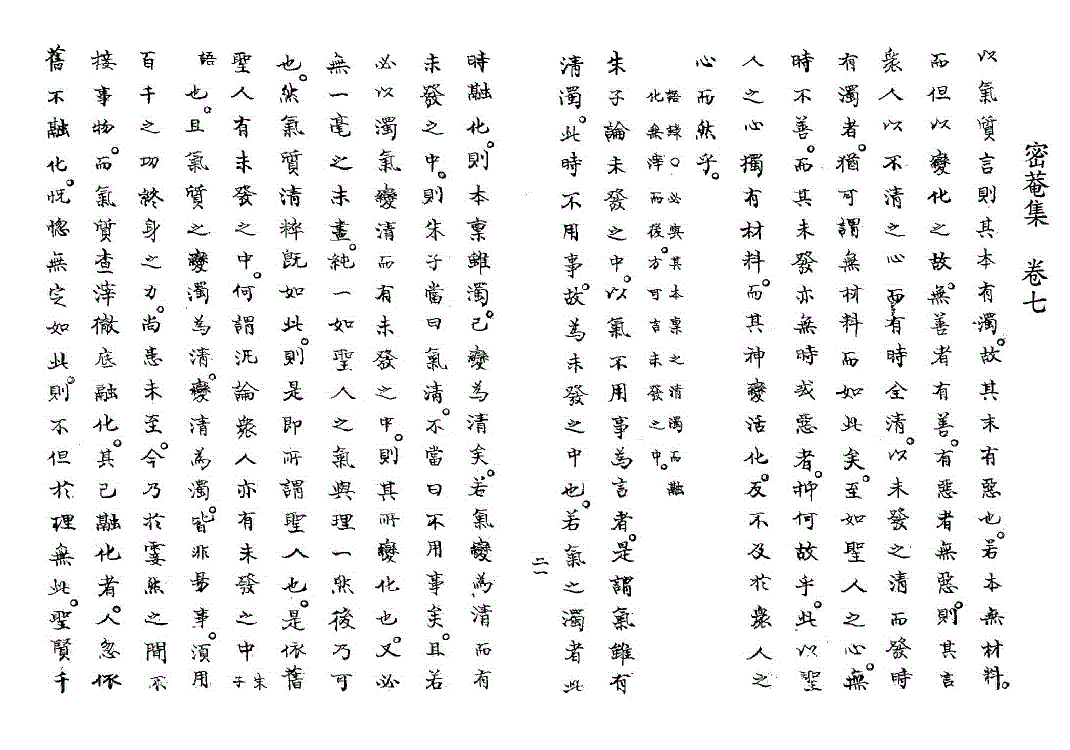 以气质言则其本有浊。故其末有恶也。若本无材料。而但以变化之故。无善者有善。有恶者无恶。则其言众人以不清之心而有时全清。以未发之清而发时有浊者。犹可谓无材料而如此矣。至如圣人之心。无时不善。而其未发亦无时或恶者。抑何故乎。此以圣人之心独有材料。而其神变活化。反不及于众人之心而然乎。
以气质言则其本有浊。故其末有恶也。若本无材料。而但以变化之故。无善者有善。有恶者无恶。则其言众人以不清之心而有时全清。以未发之清而发时有浊者。犹可谓无材料而如此矣。至如圣人之心。无时不善。而其未发亦无时或恶者。抑何故乎。此以圣人之心独有材料。而其神变活化。反不及于众人之心而然乎。(语录○必与其本禀之清浊而融化无滓而后。方可言未发之中。)
朱子论未发之中。以气不用事为言者。是谓气虽有清浊。此时不用事。故为未发之中也。若气之浊者此时融化。则本禀虽浊。已变为清矣。若气变为清而有未发之中。则朱子当曰气清。不当曰不用事矣。且若必以浊气变清而有未发之中。则其所变化也。又必无一毫之未尽。纯一如圣人之气与理一然后乃可也。然气质清粹既如此。则是即所谓圣人也。是依旧圣人有未发之中。何谓汎论众人亦有未发之中(朱子语)也。且气质之变浊为清。变清为浊。皆非易事。须用百千之功终身之力。尚患未至。今乃于霎然之间不接事物。而气质查滓彻底融化。其已融化者。人忽依旧不融化。恍惚无定如此。则不但于理无此。圣贤千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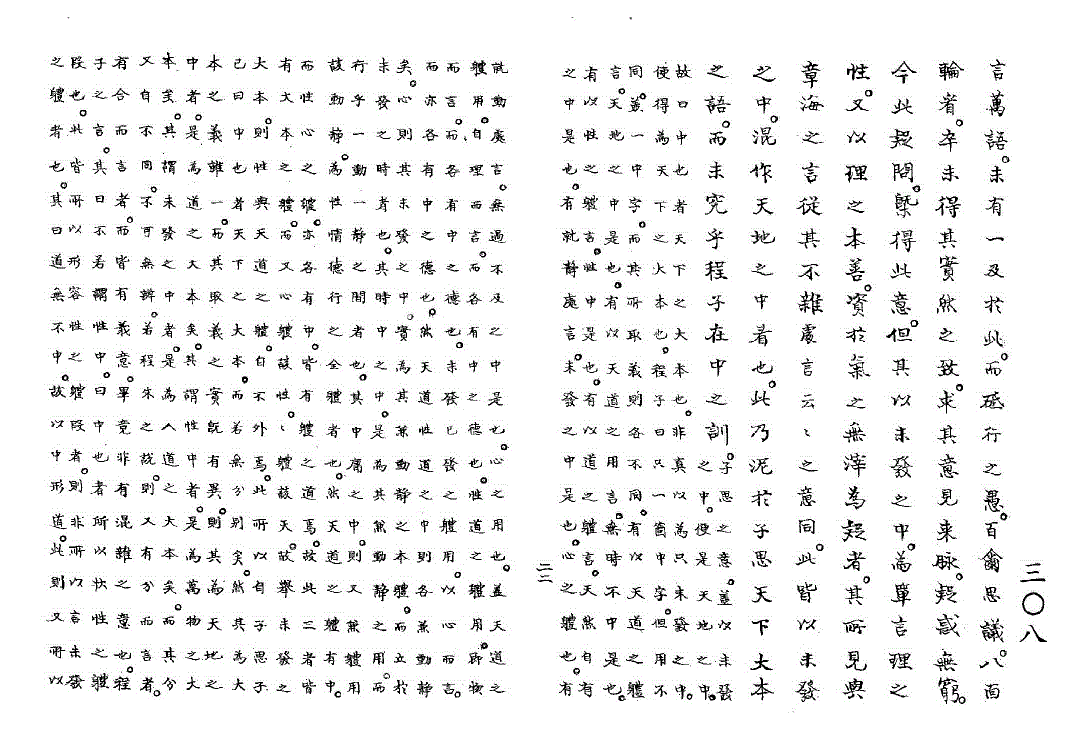 言万语。未有一及于此。而砥行之愚。百尔思议。八面轮看。卒未得其实然之致。求其意见来脉。疑惑无穷。今此疑问。槩得此意。但其以未发之中。为单言理之性。又以理之本善。资于气之无滓为疑者。其所见与章海之言从其不杂处言云云之意同。此皆以未发之中。混作天地之中看也。此乃泥于子思天下大本之语。而未究乎程子在中之训。(子思之意。盖以未发之中。便是天地之中。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非真以为只未发之中。便得为天下之大本也。程子曰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盖一中字。而其所取义则各不同。有以天道之体言。天地之中是也。有以天道之用言。无时不中是也。有以性之体言。性中是也。有以道之体言。天然自有之中是也。有就静处言。未发之中是也。心之体也。有就动处言。无过不及之中是也。心之用也。盖天道之体用。自理而言。而各有中之德也。性道之体用。即物而言。而各有中之德也。未发已发之体用。以心而言。而亦各有中之德也。然天道性道之中则各兼动静矣。心则其未发之中。实为其兼动静之本体。而立于未发之时者也。其时中之中。是为其兼动静之用。而行乎一动一静之间者也。其中庸之中。则又兼体用该动静。为性情德行之全体者也。然天道之体有中。而性心之体。亦各有中。皆有体之道焉。故此三者皆有大本之体。而又心体该性。性体该天。故举未发之大本。则性与天道之体。自不外焉。此所以自子思子已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若无分别矣。然其为大本之义虽一。而其取义之实既有异。则其为天地之中者。是为道之大本矣。其谓性中者。是为万物之大本矣。其谓未发之中者。是为人道之大本矣。而其分又自不同。不可无辨。若程朱之说。则又有分而言者。有合而言者。而皆有义意。毕竟非有混杂之意也。程子之言。其曰不若谓性中。曰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此皆所以形容性之体段者。则非所以言未发之体者也。其曰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此则又所以
言万语。未有一及于此。而砥行之愚。百尔思议。八面轮看。卒未得其实然之致。求其意见来脉。疑惑无穷。今此疑问。槩得此意。但其以未发之中。为单言理之性。又以理之本善。资于气之无滓为疑者。其所见与章海之言从其不杂处言云云之意同。此皆以未发之中。混作天地之中看也。此乃泥于子思天下大本之语。而未究乎程子在中之训。(子思之意。盖以未发之中。便是天地之中。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非真以为只未发之中。便得为天下之大本也。程子曰只一个中字。但用不同。盖一中字。而其所取义则各不同。有以天道之体言。天地之中是也。有以天道之用言。无时不中是也。有以性之体言。性中是也。有以道之体言。天然自有之中是也。有就静处言。未发之中是也。心之体也。有就动处言。无过不及之中是也。心之用也。盖天道之体用。自理而言。而各有中之德也。性道之体用。即物而言。而各有中之德也。未发已发之体用。以心而言。而亦各有中之德也。然天道性道之中则各兼动静矣。心则其未发之中。实为其兼动静之本体。而立于未发之时者也。其时中之中。是为其兼动静之用。而行乎一动一静之间者也。其中庸之中。则又兼体用该动静。为性情德行之全体者也。然天道之体有中。而性心之体。亦各有中。皆有体之道焉。故此三者皆有大本之体。而又心体该性。性体该天。故举未发之大本。则性与天道之体。自不外焉。此所以自子思子已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若无分别矣。然其为大本之义虽一。而其取义之实既有异。则其为天地之中者。是为道之大本矣。其谓性中者。是为万物之大本矣。其谓未发之中者。是为人道之大本矣。而其分又自不同。不可无辨。若程朱之说。则又有分而言者。有合而言者。而皆有义意。毕竟非有混杂之意也。程子之言。其曰不若谓性中。曰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此皆所以形容性之体段者。则非所以言未发之体者也。其曰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此则又所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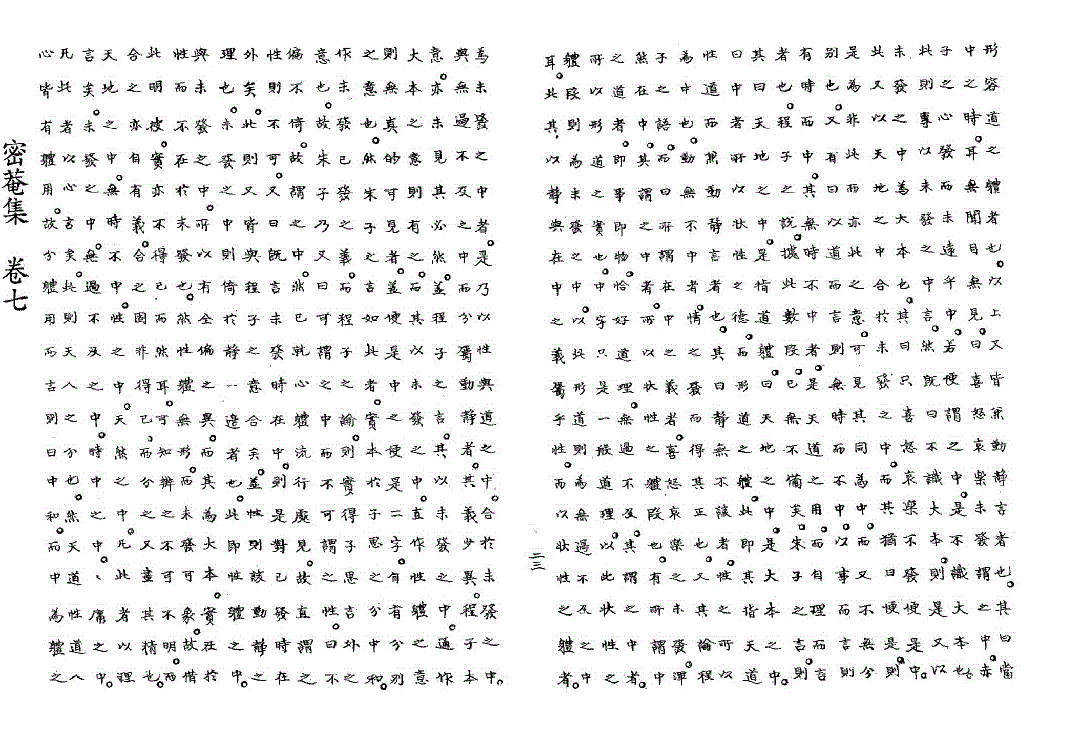 形容道之体者也。以上又皆兼动静言者也。其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赤子之心发而未远乎中。若便谓之中。是不识大本也。此则专以未发之中言。然既曰不识大本。则是又以未发之中为大本也。其曰只喜怒哀乐不发便是中。此又以天地之中合于未发之中。而其犹曰便是。则是为非此而亦此之意。可见其同为中。而又不无分别也。又有曰以道而言则无时而不中。以事而言则有时而中。其无时不中者。是天道之用。而自理而言者也。程子之说。据此数段。已无不备矣。朱子之言。则其曰天地之中。是指道体。曰天地之中。是大本之中。曰中者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此即其指天道性道而兼动静言者也。其曰静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动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又其论程子之语。而曰所谓在中之义者。喜怒哀乐之未发。浑然在中。其谓之中者。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有所谓中之道者。即事即物。恰好道理。无过不及。其谓之中者。所以形道之实也。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状性之体段则为未发之中。以此形道则为无过不及之中耳。此其以静与在中之义属乎性。而以状性之体者。为未发之中者。是乃以性与道之中。合于未发之中。与无过不及之中而分属动静者。其义少异。程子本意。亦未见其必然。盖程子之言。其以未发之中。通作大本之意则有之。而其以未发之中。直作性体之意则无真的可见者。盖便是中之便是二字。自有分别之意也。然朱子之言如此者。实本于子思之分中和。作未发已发之义。而程子之论。则实得子思言外之意也。故朱子乃又曰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曰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又曰既言未发时在中。则是对已发时在外矣。此则又皆与程子之意合矣。盖性则该动静之理也。未发之中则倚于静一边者也。此即性体之中。与未发之中。所以有全偏之异。而其为大本。实在于性而不在于未发也。然性体无形。而未发可象。故借此明彼。实亦不得已而然耳。可知辨之不可不明。而合之亦自有义。合之固非得已。而分之又尽其精也。天地之中。无时不中。性之中。天然之中。凡此者以理言矣。未发之中。无过不及之中。时中之中。中庸之中。凡此者以心言矣。此则天人之分也。然天道性道人心皆有体用。故分体用而言则曰中和。而中为体之
形容道之体者也。以上又皆兼动静言者也。其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赤子之心发而未远乎中。若便谓之中。是不识大本也。此则专以未发之中言。然既曰不识大本。则是又以未发之中为大本也。其曰只喜怒哀乐不发便是中。此又以天地之中合于未发之中。而其犹曰便是。则是为非此而亦此之意。可见其同为中。而又不无分别也。又有曰以道而言则无时而不中。以事而言则有时而中。其无时不中者。是天道之用。而自理而言者也。程子之说。据此数段。已无不备矣。朱子之言。则其曰天地之中。是指道体。曰天地之中。是大本之中。曰中者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此即其指天道性道而兼动静言者也。其曰静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动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又其论程子之语。而曰所谓在中之义者。喜怒哀乐之未发。浑然在中。其谓之中者。所以状性之体段也。有所谓中之道者。即事即物。恰好道理。无过不及。其谓之中者。所以形道之实也。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状性之体段则为未发之中。以此形道则为无过不及之中耳。此其以静与在中之义属乎性。而以状性之体者。为未发之中者。是乃以性与道之中。合于未发之中。与无过不及之中而分属动静者。其义少异。程子本意。亦未见其必然。盖程子之言。其以未发之中。通作大本之意则有之。而其以未发之中。直作性体之意则无真的可见者。盖便是中之便是二字。自有分别之意也。然朱子之言如此者。实本于子思之分中和。作未发已发之义。而程子之论。则实得子思言外之意也。故朱子乃又曰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曰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又曰既言未发时在中。则是对已发时在外矣。此则又皆与程子之意合矣。盖性则该动静之理也。未发之中则倚于静一边者也。此即性体之中。与未发之中。所以有全偏之异。而其为大本。实在于性而不在于未发也。然性体无形。而未发可象。故借此明彼。实亦不得已而然耳。可知辨之不可不明。而合之亦自有义。合之固非得已。而分之又尽其精也。天地之中。无时不中。性之中。天然之中。凡此者以理言矣。未发之中。无过不及之中。时中之中。中庸之中。凡此者以心言矣。此则天人之分也。然天道性道人心皆有体用。故分体用而言则曰中和。而中为体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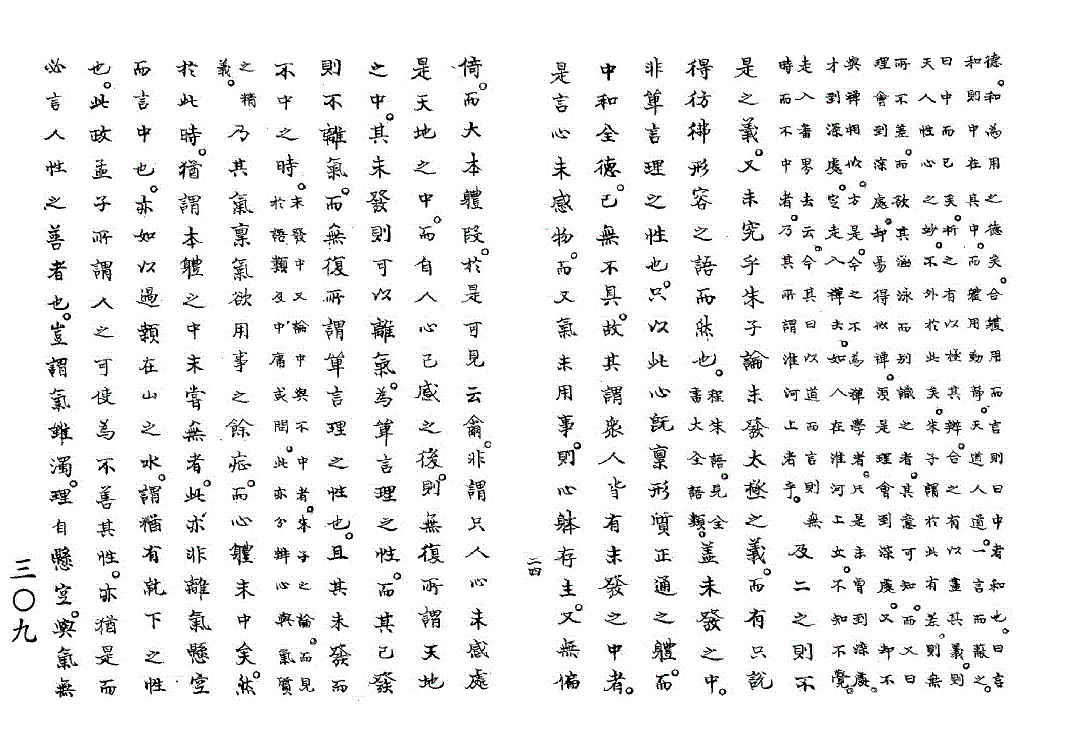 德。和为用之德矣。合体用而言则曰中者和也。曰言和则中在其中。而体用动静。天道人道。一言而蔽之。曰中而已矣。析之有以极其辨。合之有以尽其义。则天人性心之妙。不外于此矣。朱子谓于此有差。则无所不差。而欲其涵泳而别识之者。其意可知。而又曰理会到深处。却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云。今其曰以道而言则无时而不中者。乃其所谓淮河上者乎。)及二之则不是之义。又未究乎朱子论未发太极之义。而有只说得彷佛形容之语而然也。(程朱语。见全书大全语类。)盖未发之中。非单言理之性也。只以此心既禀形质正通之体。而中和全德。已无不具。故其谓众人皆有未发之中者。是言心未感物。而又气未用事。则心体存主。又无偏倚。而大本体段。于是可见云尔。非谓只人心未感处是天地之中。而自人心已感之后。则无复所谓天地之中。其未发则可以离气。为单言理之性。而其已发则不离气。而无复所谓单言理之性也。且其未发而不中之时。(未发中又论中与不中者。朱子之论。而见于语类及中庸或问。此亦分辨心与气质之精义。)乃其气禀气欲用事之馀症。而心体未中矣。然于此时。犹谓本体之中未尝无者。此亦非离气悬空而言中也。亦如以过颡在山之水。谓犹有就下之性也。此政孟子所谓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而必言人性之善者也。岂谓气虽浊。理自悬空。与气无
德。和为用之德矣。合体用而言则曰中者和也。曰言和则中在其中。而体用动静。天道人道。一言而蔽之。曰中而已矣。析之有以极其辨。合之有以尽其义。则天人性心之妙。不外于此矣。朱子谓于此有差。则无所不差。而欲其涵泳而别识之者。其意可知。而又曰理会到深处。却易得似禅。须是理会到深处。又却不与禅相似。方是。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觉。走入番界去云。今其曰以道而言则无时而不中者。乃其所谓淮河上者乎。)及二之则不是之义。又未究乎朱子论未发太极之义。而有只说得彷佛形容之语而然也。(程朱语。见全书大全语类。)盖未发之中。非单言理之性也。只以此心既禀形质正通之体。而中和全德。已无不具。故其谓众人皆有未发之中者。是言心未感物。而又气未用事。则心体存主。又无偏倚。而大本体段。于是可见云尔。非谓只人心未感处是天地之中。而自人心已感之后。则无复所谓天地之中。其未发则可以离气。为单言理之性。而其已发则不离气。而无复所谓单言理之性也。且其未发而不中之时。(未发中又论中与不中者。朱子之论。而见于语类及中庸或问。此亦分辨心与气质之精义。)乃其气禀气欲用事之馀症。而心体未中矣。然于此时。犹谓本体之中未尝无者。此亦非离气悬空而言中也。亦如以过颡在山之水。谓犹有就下之性也。此政孟子所谓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而必言人性之善者也。岂谓气虽浊。理自悬空。与气无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0H 页
 所干涉。而自在其为中耶。勉斋之言。虽有未莹。(勉斋语。即所谓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有嬴乏。而理则无胜负之语。)其本意实不如此。(今以未发之中为单言理之性者。似据所谓理自正理无胜负之语而言也。)政不可以辞害意。以益其疾也。盖其所谓理自正之理。即以乐记所谓天之性。(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朱子所谓浑是天理(朱子释乐记之语曰。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又曰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所谓中者状性之体。正于此见之。此一则答胡广仲书。一则答林择之书。而皆以此为未发之中也。)者。言只以此时私欲未萌。故谓之天性天理也。是对欲言之理也。非对形而下之理也。故未发中体只是气质不用事。而心之本体。虚明湛一。故无人欲之杂。而谓之天性。谓之天理。全具则是谓之中也。盖此心不为气禀之蔽物欲之累。然后方是天理。而此天理于此心未发则谓之中。于此心已发则谓之和。故朱子以心之所存言矣。岂谓此时此心虽偏且有赢乏。而其形而上之性独自正。且无胜负耶。此等名义例不加精覈。乃以为全然无资于气而性自纯一云则可乎。除非圣人之言。自易有太极。形而上之谓道。一阴而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下。至程子冲漠无朕。朱子未有此气。已有此性云云。卒无言无气悬空之理。(程朱语须精看。才见得不悬空。)悬空言
所干涉。而自在其为中耶。勉斋之言。虽有未莹。(勉斋语。即所谓方其未发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则气虽偏而理自正。气虽有嬴乏。而理则无胜负之语。)其本意实不如此。(今以未发之中为单言理之性者。似据所谓理自正理无胜负之语而言也。)政不可以辞害意。以益其疾也。盖其所谓理自正之理。即以乐记所谓天之性。(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朱子所谓浑是天理(朱子释乐记之语曰。当此之时。心之所存。浑是天理。未有人欲之伪。故曰天之性。又曰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所谓中者状性之体。正于此见之。此一则答胡广仲书。一则答林择之书。而皆以此为未发之中也。)者。言只以此时私欲未萌。故谓之天性天理也。是对欲言之理也。非对形而下之理也。故未发中体只是气质不用事。而心之本体。虚明湛一。故无人欲之杂。而谓之天性。谓之天理。全具则是谓之中也。盖此心不为气禀之蔽物欲之累。然后方是天理。而此天理于此心未发则谓之中。于此心已发则谓之和。故朱子以心之所存言矣。岂谓此时此心虽偏且有赢乏。而其形而上之性独自正。且无胜负耶。此等名义例不加精覈。乃以为全然无资于气而性自纯一云则可乎。除非圣人之言。自易有太极。形而上之谓道。一阴而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以下。至程子冲漠无朕。朱子未有此气。已有此性云云。卒无言无气悬空之理。(程朱语须精看。才见得不悬空。)悬空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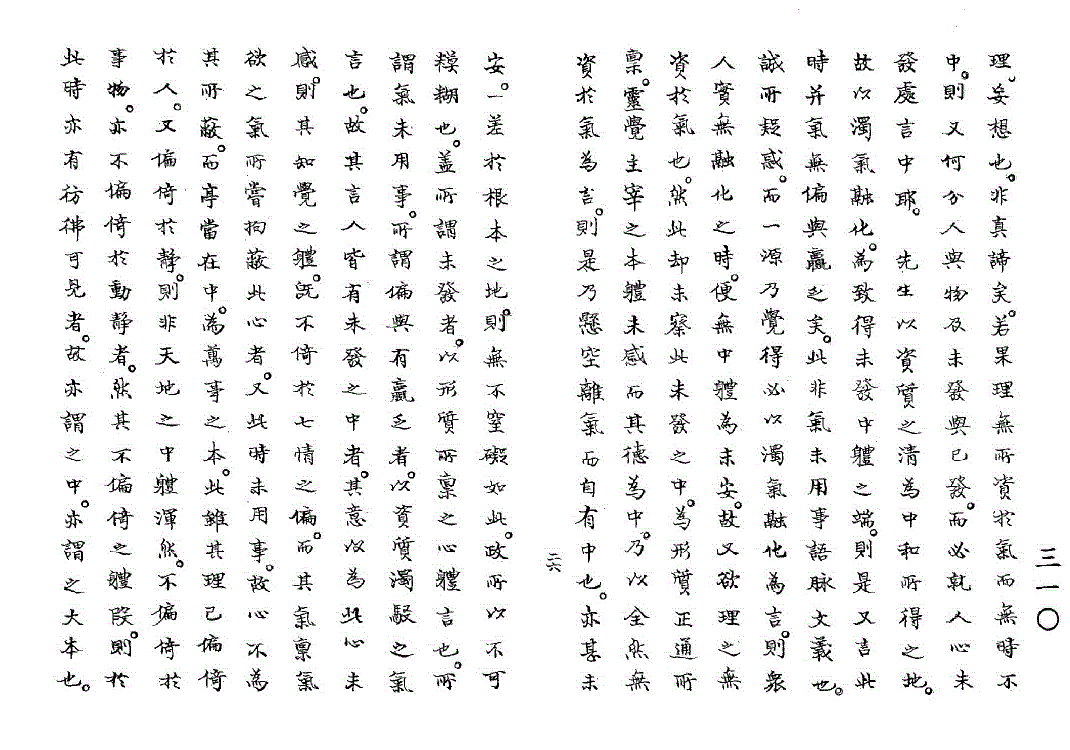 理。妄想也。非真谛矣。若果理无所资于气而无时不中。则又何分人与物及未发与已发。而必就人心未发处言中耶。 先生以资质之清为中和所得之地。故以浊气融化。为致得未发中体之端。则是又言此时并气无偏与赢乏矣。此非气未用事语脉文义也。诚所疑惑。而一源乃觉得必以浊气融化为言。则众人实无融化之时。便无中体为未安。故又欲理之无资于气也。然此却未察此未发之中。为形质正通所禀。灵觉主宰之本体未感而其德为中。乃以全然无资于气为言。则是乃悬空离气而自有中也。亦甚未安。一差于根本之地。则无不窒碍如此。政所以不可模糊也。盖所谓未发者。以形质所禀之心体言也。所谓气未用事。所谓偏与有赢乏者。以资质浊驳之气言也。故其言人皆有未发之中者。其意以为此心未感。则其知觉之体。既不倚于七情之偏。而其气禀气欲之气所尝拘蔽此心者。又此时未用事。故心不为其所蔽。而亭当在中。为万事之本。此虽其理已偏倚于人。又偏倚于静。则非天地之中体浑然。不偏倚于事物。亦不偏倚于动静者。然其不偏倚之体段。则于此时亦有彷佛可见者。故亦谓之中。亦谓之大本也。
理。妄想也。非真谛矣。若果理无所资于气而无时不中。则又何分人与物及未发与已发。而必就人心未发处言中耶。 先生以资质之清为中和所得之地。故以浊气融化。为致得未发中体之端。则是又言此时并气无偏与赢乏矣。此非气未用事语脉文义也。诚所疑惑。而一源乃觉得必以浊气融化为言。则众人实无融化之时。便无中体为未安。故又欲理之无资于气也。然此却未察此未发之中。为形质正通所禀。灵觉主宰之本体未感而其德为中。乃以全然无资于气为言。则是乃悬空离气而自有中也。亦甚未安。一差于根本之地。则无不窒碍如此。政所以不可模糊也。盖所谓未发者。以形质所禀之心体言也。所谓气未用事。所谓偏与有赢乏者。以资质浊驳之气言也。故其言人皆有未发之中者。其意以为此心未感。则其知觉之体。既不倚于七情之偏。而其气禀气欲之气所尝拘蔽此心者。又此时未用事。故心不为其所蔽。而亭当在中。为万事之本。此虽其理已偏倚于人。又偏倚于静。则非天地之中体浑然。不偏倚于事物。亦不偏倚于动静者。然其不偏倚之体段。则于此时亦有彷佛可见者。故亦谓之中。亦谓之大本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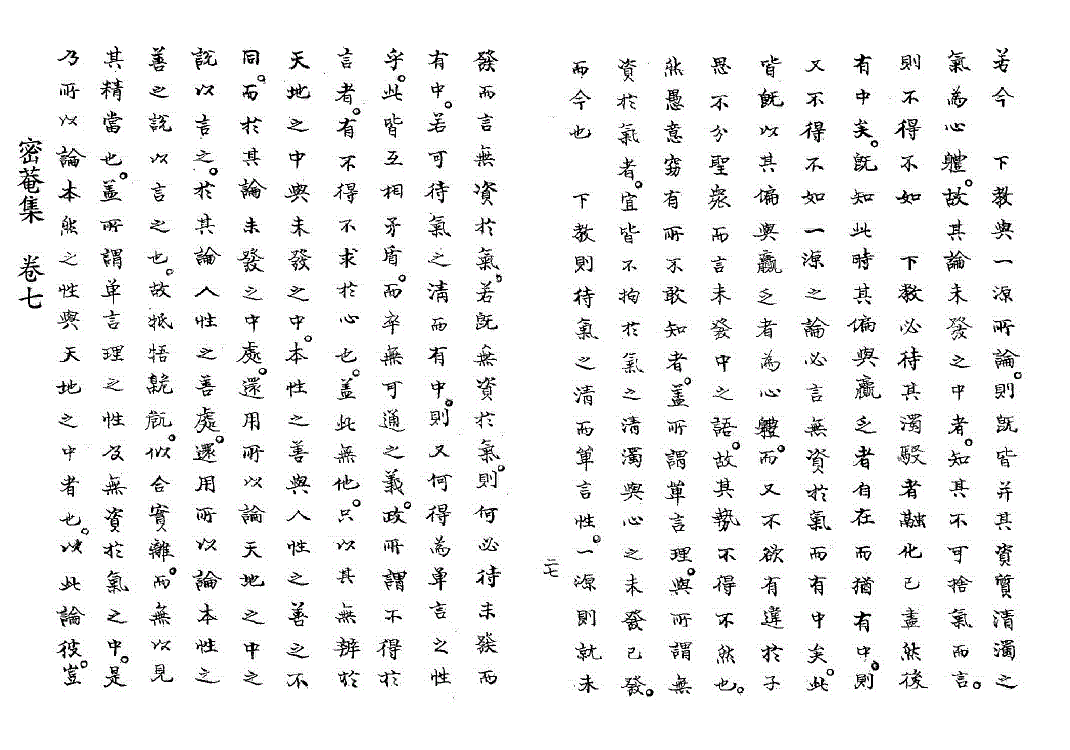 若今 下教与一源所论。则既皆并其资质清浊之气为心体。故其论未发之中者。知其不可舍气而言。则不得不如 下教必待其浊驳者融化已尽然后有中矣。既知此时其偏与赢乏者自在而犹有中。则又不得不如一源之论必言无资于气而有中矣。此皆既以其偏与赢乏者为心体。而又不欲有违于子思不分圣众而言未发中之语。故其势不得不然也。然愚意窃有所不敢知者。盖所谓单言理。与所谓无资于气者。宜皆不拘于气之清浊与心之未发已发。而今也 下教则待气之清而单言性。一源则就未发而言无资于气。若既无资于气。则何必待未发而有中。若可待气之清而有中。则又何得为单言之性乎。此皆互相矛盾。而卒无可通之义。政所谓不得于言者。有不得不求于心也。盖此无他。只以其无辨于天地之中与未发之中。本性之善与人性之善之不同。而于其论未发之中处。还用所以论天地之中之说以言之。于其论人性之善处。还用所以论本性之善之说以言之也。故牴牾臲𠨜。似合实离。而无以见其精当也。盖所谓单言理之性及无资于气之中。是乃所以论本然之性与天地之中者也。以此论彼。岂
若今 下教与一源所论。则既皆并其资质清浊之气为心体。故其论未发之中者。知其不可舍气而言。则不得不如 下教必待其浊驳者融化已尽然后有中矣。既知此时其偏与赢乏者自在而犹有中。则又不得不如一源之论必言无资于气而有中矣。此皆既以其偏与赢乏者为心体。而又不欲有违于子思不分圣众而言未发中之语。故其势不得不然也。然愚意窃有所不敢知者。盖所谓单言理。与所谓无资于气者。宜皆不拘于气之清浊与心之未发已发。而今也 下教则待气之清而单言性。一源则就未发而言无资于气。若既无资于气。则何必待未发而有中。若可待气之清而有中。则又何得为单言之性乎。此皆互相矛盾。而卒无可通之义。政所谓不得于言者。有不得不求于心也。盖此无他。只以其无辨于天地之中与未发之中。本性之善与人性之善之不同。而于其论未发之中处。还用所以论天地之中之说以言之。于其论人性之善处。还用所以论本性之善之说以言之也。故牴牾臲𠨜。似合实离。而无以见其精当也。盖所谓单言理之性及无资于气之中。是乃所以论本然之性与天地之中者也。以此论彼。岂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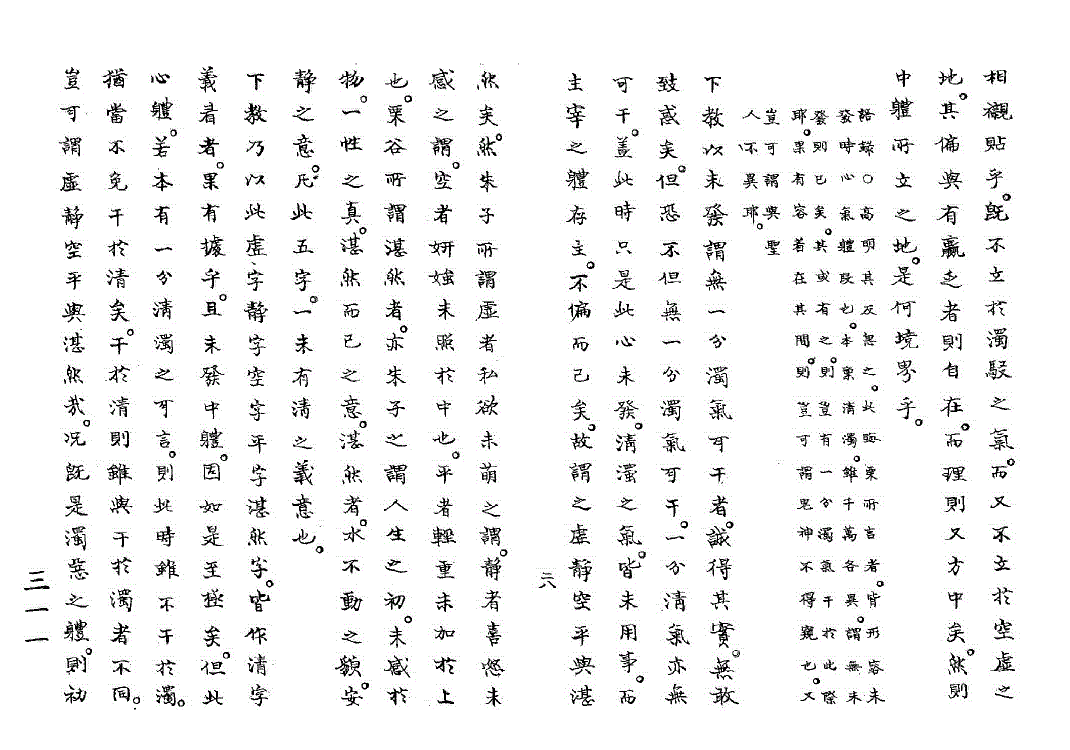 相衬贴乎。既不立于浊驳之气。而又不立于空虚之地。其偏与有赢乏者则自在。而理则又方中矣。然则中体所立之地。是何境界乎。
相衬贴乎。既不立于浊驳之气。而又不立于空虚之地。其偏与有赢乏者则自在。而理则又方中矣。然则中体所立之地。是何境界乎。(语录○高明其反思之。此晦栗所言者。皆所容未发时心气体段也。本禀清浊。虽千万各异。谓无未发则已矣。其或有之。则岂有一分浊气干于此际耶。果有容着在其间。则岂可谓鬼神不得窥也。又岂可谓与圣人不异耶。)
下教以未发谓无一分浊气可干者。诚得其实。无敢致惑矣。但恐不但无一分浊气可干。一分清气亦无可干。盖此时只是此心未发。清浊之气。皆未用事。而主宰之体存主。不偏而已矣。故谓之虚静空平与湛然矣。然朱子所谓虚者私欲未萌之谓。静者喜怒未感之谓。空者妍媸未照于中也。平者轻重未加于上也。栗谷所谓湛然者。亦朱子之谓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之意。湛然者。水不动之貌。安静之意。凡此五字。一未有清之义意也。
下教乃以此虚字静字空字平字湛然字。皆作清字义看者。果有据乎。且未发中体。固如是至极矣。但此心体。若本有一分清浊之可言。则此时虽不干于浊。犹当不免干于清矣。干于清则虽与干于浊者不同。岂可谓虚静空平与湛然哉。况既是浊恶之体。则初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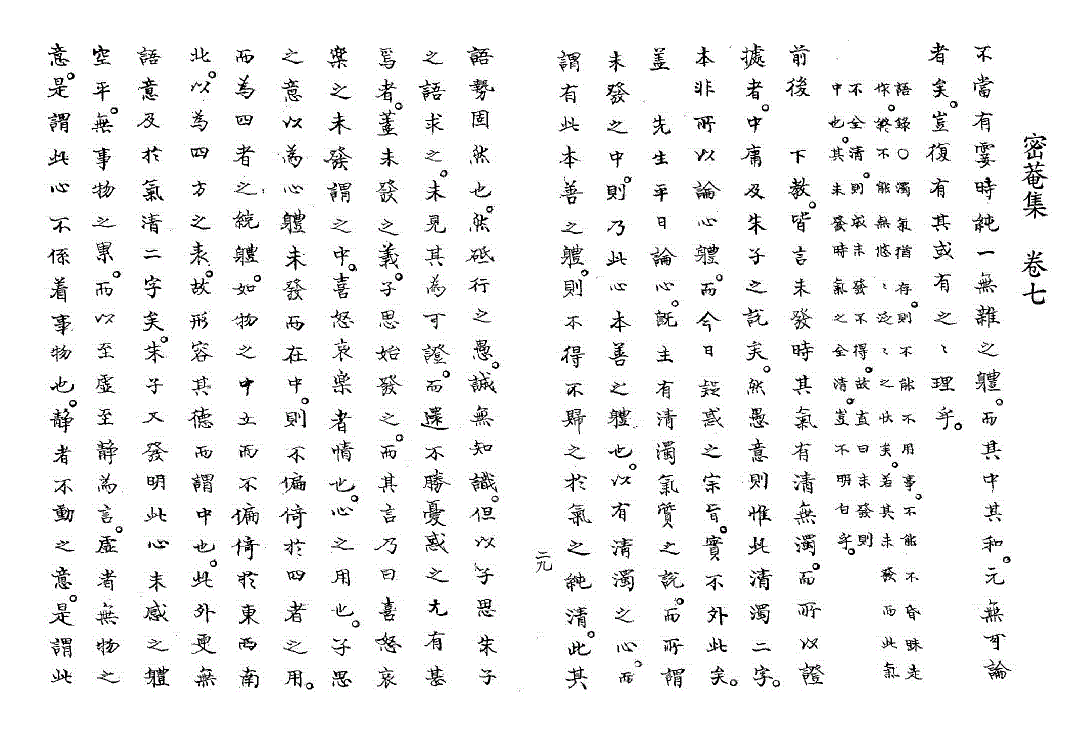 不当有霎时纯一无杂之体。而其中其和。元无可论者矣。岂复有其或有之之理乎。
不当有霎时纯一无杂之体。而其中其和。元无可论者矣。岂复有其或有之之理乎。(语录○浊气犹存。则不能不用事。不能不昏昧走作。终不能无悠悠泛泛之状矣。若其未发而此气不全清。则成未发不得。故直曰未发则中也。其未发时气之全清。岂不明白乎。)
前后 下教。皆言未发时其气有清无浊。而所以證据者。中庸及朱子之说矣。然愚意则惟此清浊二字。本非所以论心体。而今日疑惑之宗旨。实不外此矣。盖 先生平日论心。既主有清浊气质之说。而所谓未发之中。则乃此心本善之体也。以有清浊之心。而谓有此本善之体。则不得不归之于气之纯清。此其语势固然也。然砥行之愚。诚无知识。但以子思朱子之语求之。未见其为可證。而还不胜忧惑之尤有甚焉者。盖未发之义。子思始发之。而其言乃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者情也。心之用也。子思之意以为心体未发而在中。则不偏倚于四者之用。而为四者之统体。如物之中立而不偏倚于东西南北。以为四方之表。故形容其德而谓中也。此外更无语意及于气清二字矣。朱子又发明此心未感之体空平。无事物之累。而以至虚至静为言。虚者无物之意。是谓此心不系着事物也。静者不动之意。是谓此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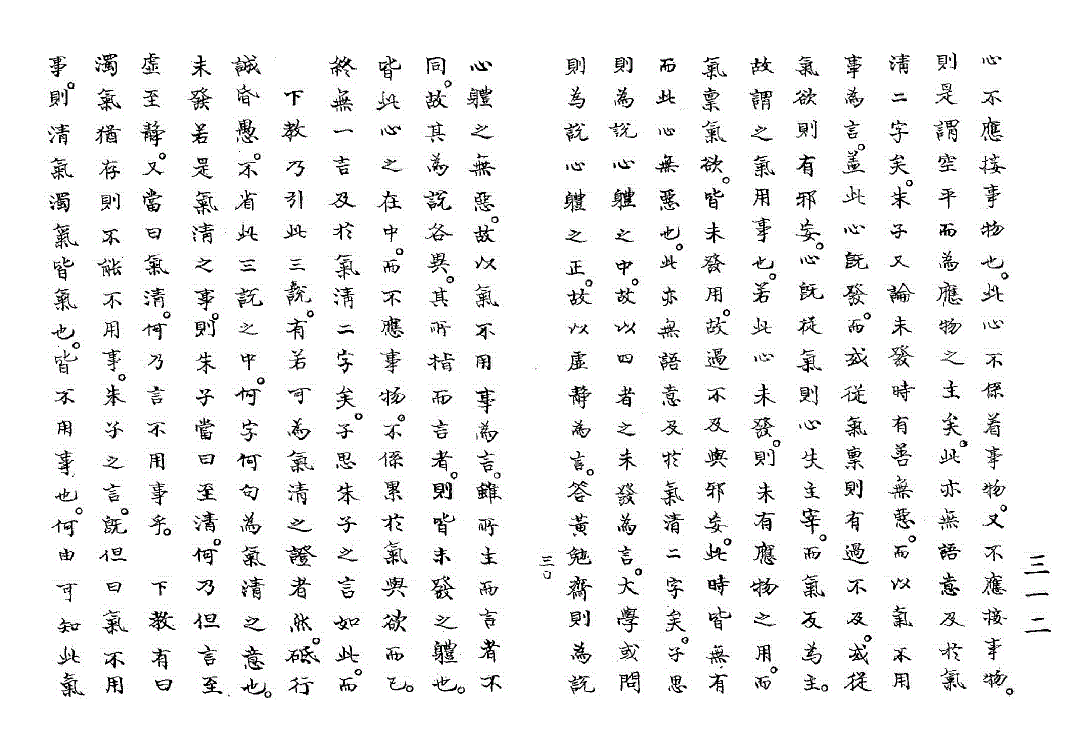 心不应接事物也。此心不系着事物。又不应接事物。则是谓空平而为应物之主矣。此亦无语意及于气清二字矣。朱子又论未发时有善无恶。而以气不用事为言。盖此心既发。而或从气禀则有过不及。或从气欲则有邪妄。心既从气则心失主宰。而气反为主。故谓之气用事也。若此心未发。则未有应物之用。而气禀气欲。皆未发用。故过不及与邪妄。此时皆无有而此心无恶也。此亦无语意及于气清二字矣。子思则为说心体之中。故以四者之未发为言。大学或问则为说心体之正。故以虚静为言。答黄勉斋则为说心体之无恶。故以气不用事为言。虽所主而言者不同。故其为说各异。其所指而言者。则皆未发之体也。皆此心之在中。而不应事物。不系累于气与欲而已。终无一言及于气清二字矣。子思朱子之言如此。而 下教乃引此三说。有若可为气清之證者然。砥行诚昏愚。不省此三说之中。何字何句为气清之意也。未发若是气清之事。则朱子当曰至清。何乃但言至虚至静。又当曰气清。何乃言不用事乎。 下教有曰浊气犹存则不能不用事。朱子之言。既但曰气不用事。则清气浊气皆气也。皆不用事也。何由可知此气
心不应接事物也。此心不系着事物。又不应接事物。则是谓空平而为应物之主矣。此亦无语意及于气清二字矣。朱子又论未发时有善无恶。而以气不用事为言。盖此心既发。而或从气禀则有过不及。或从气欲则有邪妄。心既从气则心失主宰。而气反为主。故谓之气用事也。若此心未发。则未有应物之用。而气禀气欲。皆未发用。故过不及与邪妄。此时皆无有而此心无恶也。此亦无语意及于气清二字矣。子思则为说心体之中。故以四者之未发为言。大学或问则为说心体之正。故以虚静为言。答黄勉斋则为说心体之无恶。故以气不用事为言。虽所主而言者不同。故其为说各异。其所指而言者。则皆未发之体也。皆此心之在中。而不应事物。不系累于气与欲而已。终无一言及于气清二字矣。子思朱子之言如此。而 下教乃引此三说。有若可为气清之證者然。砥行诚昏愚。不省此三说之中。何字何句为气清之意也。未发若是气清之事。则朱子当曰至清。何乃但言至虚至静。又当曰气清。何乃言不用事乎。 下教有曰浊气犹存则不能不用事。朱子之言。既但曰气不用事。则清气浊气皆气也。皆不用事也。何由可知此气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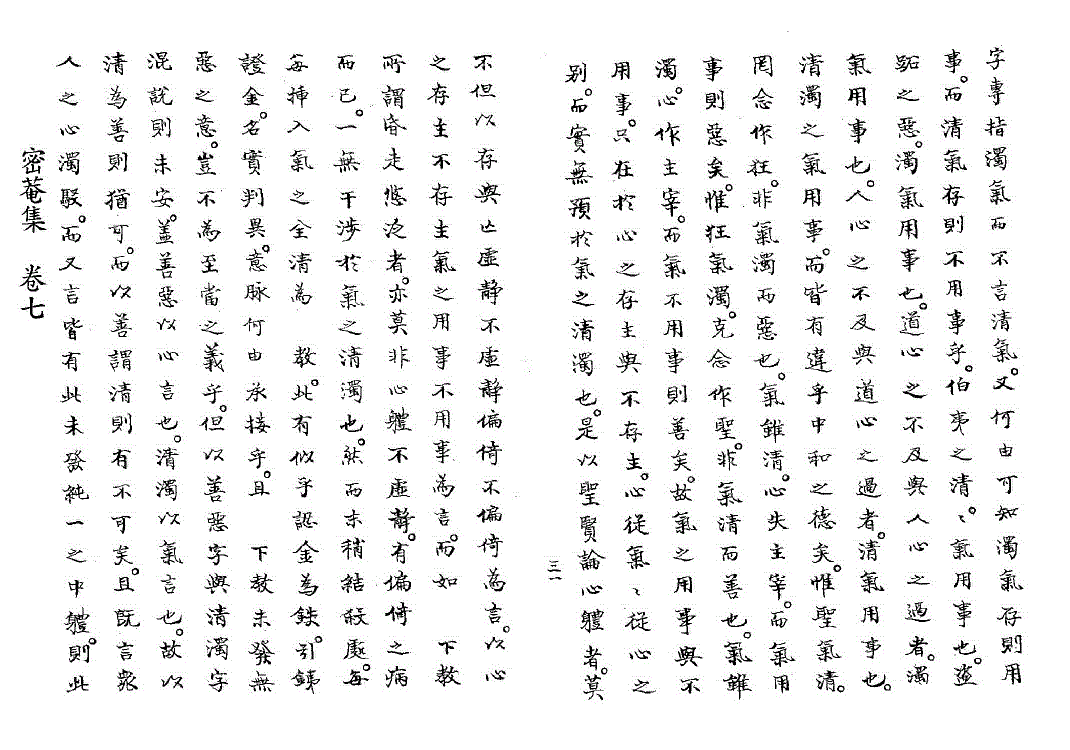 字专指浊气而不言清气。又何由可知浊气存则用事。而清气存则不用事乎。伯夷之清。清气用事也。盗蹠之恶。浊气用事也。道心之不及与人心之过者。浊气用事也。人心之不及与道心之过者。清气用事也。清浊之气用事。而皆有违乎中和之德矣。惟圣气清。罔念作狂。非气浊而恶也。气虽清。心失主宰。而气用事则恶矣。惟狂气浊。克念作圣。非气清而善也。气虽浊。心作主宰。而气不用事则善矣。故气之用事与不用事。只在于心之存主与不存主。心从气气从心之别。而实无预于气之清浊也。是以圣贤论心体者。莫不但以存与亡虚静不虚静偏倚不偏倚为言。以心之存主不存主气之用事不用事为言。而如 下教所谓昏走悠泛者。亦莫非心体不虚静。有偏倚之病而已。一无干涉于气之清浊也。然而末稍结杀处。每每插入气之全清为 教。此有似乎认金为铁。引铁證金。名实判异。意脉何由承接乎。且 下教未发无恶之意。岂不为至当之义乎。但以善恶字与清浊字混说则未安。盖善恶以心言也。清浊以气言也。故以清为善则犹可。而以善谓清则有不可矣。且既言众人之心浊驳。而又言皆有此未发纯一之中体。则此
字专指浊气而不言清气。又何由可知浊气存则用事。而清气存则不用事乎。伯夷之清。清气用事也。盗蹠之恶。浊气用事也。道心之不及与人心之过者。浊气用事也。人心之不及与道心之过者。清气用事也。清浊之气用事。而皆有违乎中和之德矣。惟圣气清。罔念作狂。非气浊而恶也。气虽清。心失主宰。而气用事则恶矣。惟狂气浊。克念作圣。非气清而善也。气虽浊。心作主宰。而气不用事则善矣。故气之用事与不用事。只在于心之存主与不存主。心从气气从心之别。而实无预于气之清浊也。是以圣贤论心体者。莫不但以存与亡虚静不虚静偏倚不偏倚为言。以心之存主不存主气之用事不用事为言。而如 下教所谓昏走悠泛者。亦莫非心体不虚静。有偏倚之病而已。一无干涉于气之清浊也。然而末稍结杀处。每每插入气之全清为 教。此有似乎认金为铁。引铁證金。名实判异。意脉何由承接乎。且 下教未发无恶之意。岂不为至当之义乎。但以善恶字与清浊字混说则未安。盖善恶以心言也。清浊以气言也。故以清为善则犹可。而以善谓清则有不可矣。且既言众人之心浊驳。而又言皆有此未发纯一之中体。则此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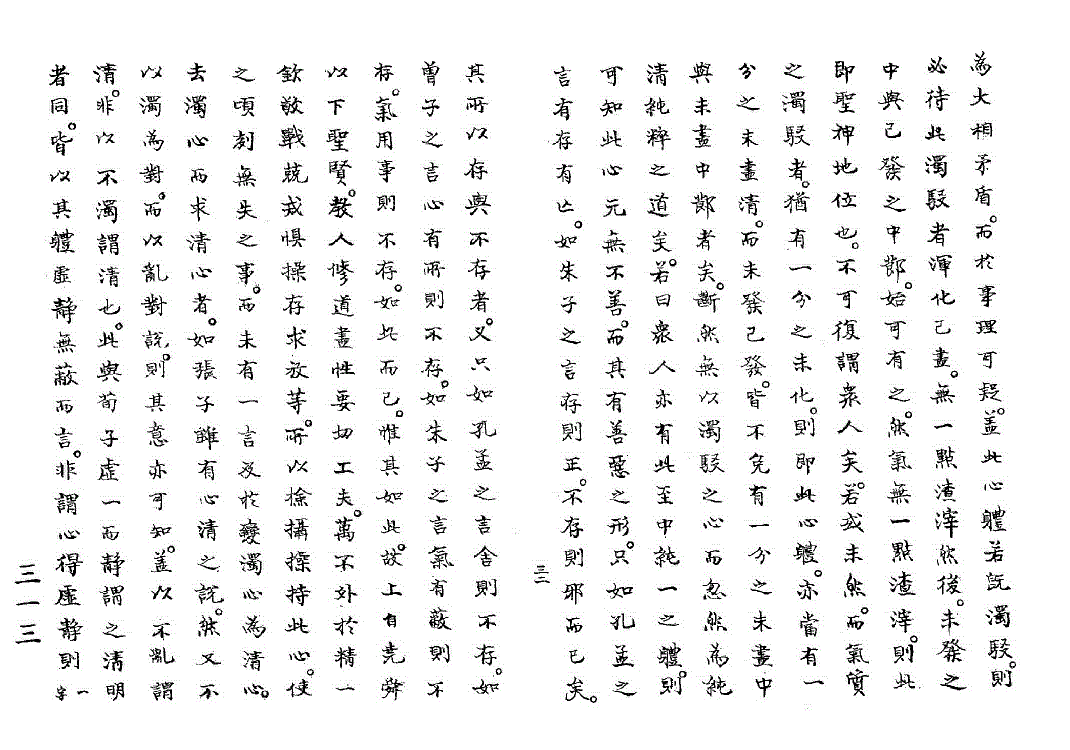 为大相矛盾。而于事理可疑。盖此心体若既浊驳。则必待此浊驳者浑化已尽。无一点渣滓然后。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节。始可有之。然气无一点渣滓。则此即圣神地位也。不可复谓众人矣。若或未然。而气质之浊驳者。犹有一分之未化。则即此心体。亦当有一分之未尽清。而未发已发。皆不免有一分之未尽中与未尽中节者矣。断然无以浊驳之心而忽然为纯清纯粹之道矣。若曰众人亦有此至中纯一之体。则可知此心元无不善。而其有善恶之形。只如孔孟之言有存有亡。如朱子之言存则正。不存则邪而已矣。其所以存与不存者。又只如孔孟之言舍则不存。如曾子之言心有所则不存。如朱子之言气有蔽则不存。气用事则不存。如此而已。惟其如此。故上自尧舜以下圣贤。教人修道尽性要切工夫。万不外于精一钦敬战兢戒惧操存求放等。所以检摄操持此心。使之顷刻无失之事。而未有一言及于变浊心为清心。去浊心而求清心者。如张子虽有心清之说。然又不以浊为对。而以乱对说。则其意亦可知。盖以不乱谓清。非以不浊谓清也。此与荀子虚一而静谓之清明者同。皆以其体虚静无蔽而言。非谓心得虚静则(一字
为大相矛盾。而于事理可疑。盖此心体若既浊驳。则必待此浊驳者浑化已尽。无一点渣滓然后。未发之中与已发之中节。始可有之。然气无一点渣滓。则此即圣神地位也。不可复谓众人矣。若或未然。而气质之浊驳者。犹有一分之未化。则即此心体。亦当有一分之未尽清。而未发已发。皆不免有一分之未尽中与未尽中节者矣。断然无以浊驳之心而忽然为纯清纯粹之道矣。若曰众人亦有此至中纯一之体。则可知此心元无不善。而其有善恶之形。只如孔孟之言有存有亡。如朱子之言存则正。不存则邪而已矣。其所以存与不存者。又只如孔孟之言舍则不存。如曾子之言心有所则不存。如朱子之言气有蔽则不存。气用事则不存。如此而已。惟其如此。故上自尧舜以下圣贤。教人修道尽性要切工夫。万不外于精一钦敬战兢戒惧操存求放等。所以检摄操持此心。使之顷刻无失之事。而未有一言及于变浊心为清心。去浊心而求清心者。如张子虽有心清之说。然又不以浊为对。而以乱对说。则其意亦可知。盖以不乱谓清。非以不浊谓清也。此与荀子虚一而静谓之清明者同。皆以其体虚静无蔽而言。非谓心得虚静则(一字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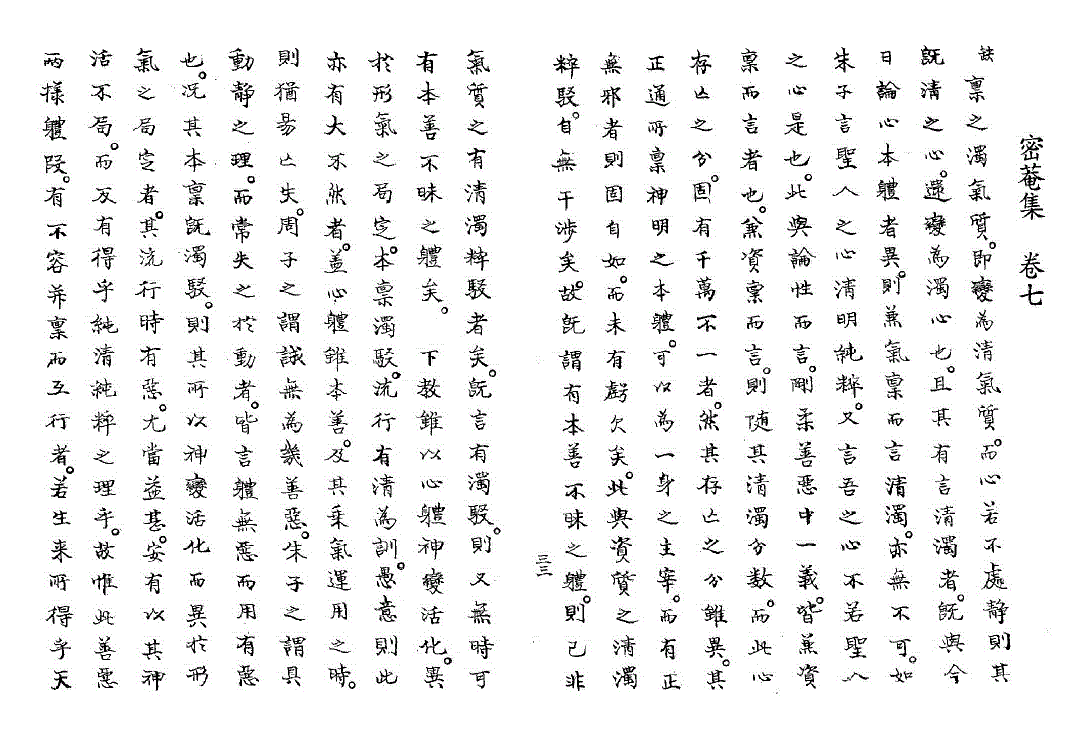 缺)禀之浊气质。即变为清气质。而心若不处静则其既清之心。还变为浊心也。且其有言清浊者。既与今日论心本体者异。则兼气禀而言清浊。亦无不可。如朱子言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又言吾之心不若圣人之心是也。此与论性而言。刚柔善恶中一义。皆兼资禀而言者也。兼资禀而言。则随其清浊分数。而此心存亡之分。固有千万不一者。然其存亡之分虽异。其正通所禀神明之本体。可以为一身之主宰。而有正无邪者则固自如。而未有亏欠矣。此与资质之清浊粹驳。自无干涉矣。故既谓有本善不昧之体。则已非气质之有清浊粹驳者矣。既言有浊驳。则又无时可有本善不昧之体矣。 下教虽以心体神变活化。异于形气之局定。本禀浊驳。流行有清为训。愚意则此亦有大不然者。盖心体虽本善。及其乘气运用之时。则犹易亡失。周子之谓诚无为几善恶。朱子之谓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者。皆言体无恶而用有恶也。况其本禀既浊驳。则其所以神变活化而异于形气之局定者。其流行时有恶。尤当益甚。安有以其神活不局。而反有得乎纯清纯粹之理乎。故惟此善恶两㨾体段。有不容并禀而互行者。若生来所得乎天
缺)禀之浊气质。即变为清气质。而心若不处静则其既清之心。还变为浊心也。且其有言清浊者。既与今日论心本体者异。则兼气禀而言清浊。亦无不可。如朱子言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又言吾之心不若圣人之心是也。此与论性而言。刚柔善恶中一义。皆兼资禀而言者也。兼资禀而言。则随其清浊分数。而此心存亡之分。固有千万不一者。然其存亡之分虽异。其正通所禀神明之本体。可以为一身之主宰。而有正无邪者则固自如。而未有亏欠矣。此与资质之清浊粹驳。自无干涉矣。故既谓有本善不昧之体。则已非气质之有清浊粹驳者矣。既言有浊驳。则又无时可有本善不昧之体矣。 下教虽以心体神变活化。异于形气之局定。本禀浊驳。流行有清为训。愚意则此亦有大不然者。盖心体虽本善。及其乘气运用之时。则犹易亡失。周子之谓诚无为几善恶。朱子之谓具动静之理。而常失之于动者。皆言体无恶而用有恶也。况其本禀既浊驳。则其所以神变活化而异于形气之局定者。其流行时有恶。尤当益甚。安有以其神活不局。而反有得乎纯清纯粹之理乎。故惟此善恶两㨾体段。有不容并禀而互行者。若生来所得乎天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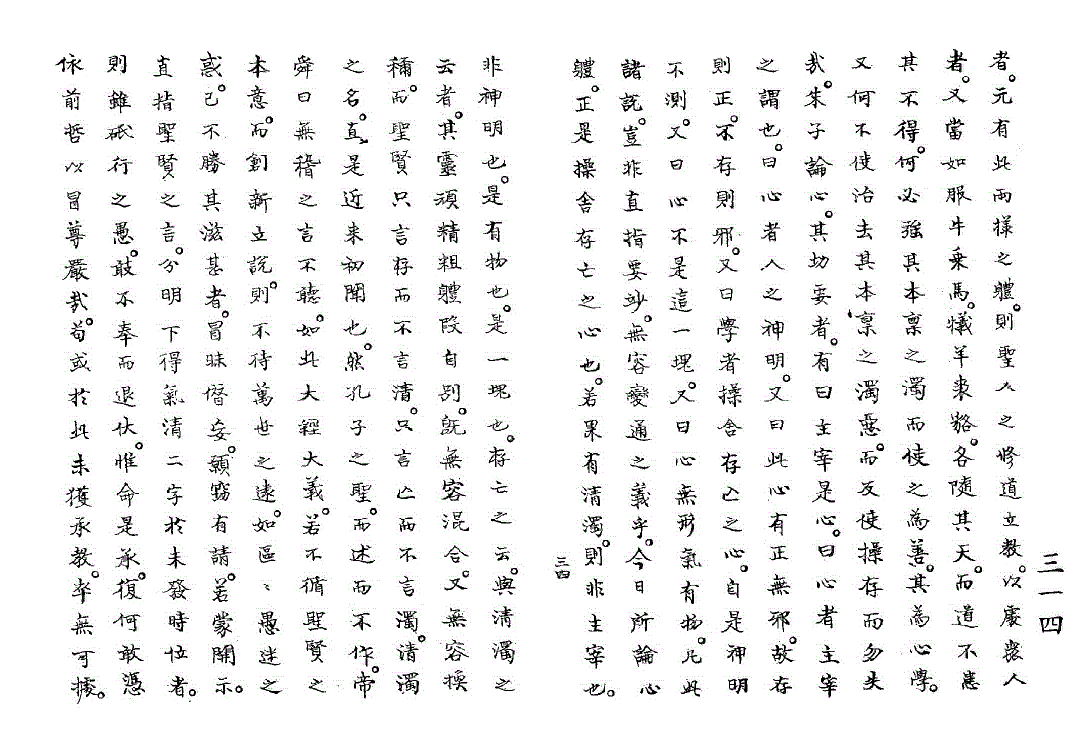 者。元有此两㨾之体。则圣人之修道立教。以处众人者。又当如服牛乘马。犠羊裘貉。各随其天。而道不患其不得。何必强其本禀之浊而使之为善。其为心学。又何不使治去其本禀之浊恶。而反使操存而勿失哉。朱子论心。其切要者。有曰主宰是心。曰心者主宰之谓也。曰心者人之神明。又曰此心有正无邪。故存则正。不存则邪。又曰学者操舍存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又曰心不是这一块。又曰心无形气有物。凡此诸说。岂非直指要妙。无容变通之义乎。今日所论心体。正是操舍存亡之心也。若果有清浊。则非主宰也。非神明也。是有物也。是一块也。存亡之云。与清浊之云者。其灵顽精粗体段自别。既无容混合。又无容换称。而圣贤只言存而不言清。只言亡而不言浊。清浊之名。直是近来初闻也。然孔子之圣。而述而不作。帝舜曰无稽之言不听。如此大经大义。若不循圣贤之本意。而创新立说。则不待万世之远。如区区愚迷之惑。已不胜其滋甚者。冒昧僭妄。愿窃有请。若蒙开示。直指圣贤之言。分明下得气清二字于未发时位者。则虽砥行之愚。敢不奉而退伏。惟命是承。复何敢凭依前哲以冒尊严哉。苟或于此未获承教。卒无可据。
者。元有此两㨾之体。则圣人之修道立教。以处众人者。又当如服牛乘马。犠羊裘貉。各随其天。而道不患其不得。何必强其本禀之浊而使之为善。其为心学。又何不使治去其本禀之浊恶。而反使操存而勿失哉。朱子论心。其切要者。有曰主宰是心。曰心者主宰之谓也。曰心者人之神明。又曰此心有正无邪。故存则正。不存则邪。又曰学者操舍存亡之心。自是神明不测。又曰心不是这一块。又曰心无形气有物。凡此诸说。岂非直指要妙。无容变通之义乎。今日所论心体。正是操舍存亡之心也。若果有清浊。则非主宰也。非神明也。是有物也。是一块也。存亡之云。与清浊之云者。其灵顽精粗体段自别。既无容混合。又无容换称。而圣贤只言存而不言清。只言亡而不言浊。清浊之名。直是近来初闻也。然孔子之圣。而述而不作。帝舜曰无稽之言不听。如此大经大义。若不循圣贤之本意。而创新立说。则不待万世之远。如区区愚迷之惑。已不胜其滋甚者。冒昧僭妄。愿窃有请。若蒙开示。直指圣贤之言。分明下得气清二字于未发时位者。则虽砥行之愚。敢不奉而退伏。惟命是承。复何敢凭依前哲以冒尊严哉。苟或于此未获承教。卒无可据。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5H 页
 而只以平日切偲之地。论心之说。主于气质。教至于解说经传。亦或参错己见。以此为教。则天灵未昧而实体难掩。圣训不容诬而所好不容阿矣。此所以反复请教。而不敢孤守恂默之为恭而已也。至如栗谷之说以为善者清气之发云云。则此与其心图圈内之气质清浊一义。而 下教之引以为据者。果有其證矣。然此亦尝以孔孟程朱之言揆之而不合。故以为不敢知而疑其为未定之论矣。盖此与孟子之养气。以为持其志存良心之助者异矣。虽其本意未必如 下教直以心体谓有清浊也。然其主气分数多。而与圣贤所说操舍存亡之义。反背已远。此间分界。正是君臣师卒人兽生死路头。有不可以毫釐差错处也。故栗谷之言。赖有圣学辑要中曰心体本正。由化于物。遂亡其正之语。自为定论。若只如文集云云之说。则栗谷大本。亦非所敢知也。
而只以平日切偲之地。论心之说。主于气质。教至于解说经传。亦或参错己见。以此为教。则天灵未昧而实体难掩。圣训不容诬而所好不容阿矣。此所以反复请教。而不敢孤守恂默之为恭而已也。至如栗谷之说以为善者清气之发云云。则此与其心图圈内之气质清浊一义。而 下教之引以为据者。果有其證矣。然此亦尝以孔孟程朱之言揆之而不合。故以为不敢知而疑其为未定之论矣。盖此与孟子之养气。以为持其志存良心之助者异矣。虽其本意未必如 下教直以心体谓有清浊也。然其主气分数多。而与圣贤所说操舍存亡之义。反背已远。此间分界。正是君臣师卒人兽生死路头。有不可以毫釐差错处也。故栗谷之言。赖有圣学辑要中曰心体本正。由化于物。遂亡其正之语。自为定论。若只如文集云云之说。则栗谷大本。亦非所敢知也。(语录○仁义礼智之性。虽于人心之虚灵不昧上言之。若尽其性则清浊分上。不可以言。故必于圣人聪明睿知之心。始有容执敬别也。)
窃以为子思所谓容执敬别者。以资质生知之禀言也。盖仁义礼智就心言。众人所同也。容执敬别从气禀言。圣人所独也。若如 下教。仁义礼智既是虚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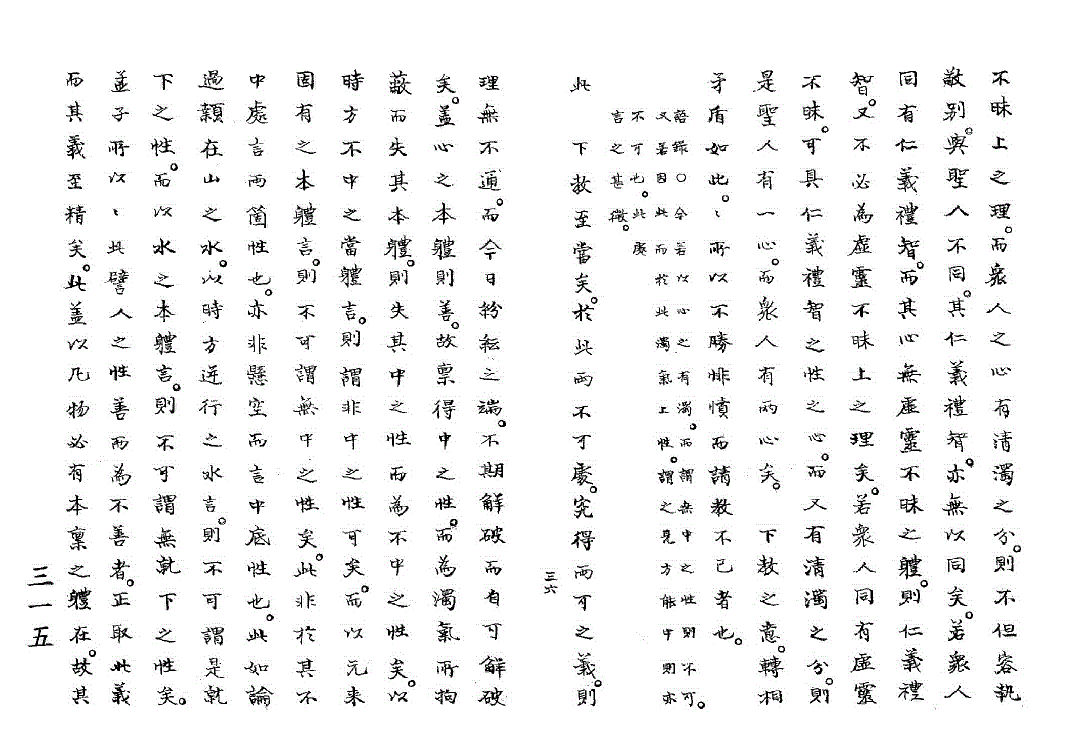 不昧上之理。而众人之心有清浊之分。则不但容执敬别。与圣人不同。其仁义礼智。亦无以同矣。若众人同有仁义礼智。而其心无虚灵不昧之体。则仁义礼智。又不必为虚灵不昧上之理矣。若众人同有虚灵不昧。可具仁义礼智之性之心。而又有清浊之分。则是圣人有一心。而众人有两心矣。 下教之意。转相矛盾如此。此所以不胜悱愤而请教不已者也。
不昧上之理。而众人之心有清浊之分。则不但容执敬别。与圣人不同。其仁义礼智。亦无以同矣。若众人同有仁义礼智。而其心无虚灵不昧之体。则仁义礼智。又不必为虚灵不昧上之理矣。若众人同有虚灵不昧。可具仁义礼智之性之心。而又有清浊之分。则是圣人有一心。而众人有两心矣。 下教之意。转相矛盾如此。此所以不胜悱愤而请教不已者也。(语录○今若以心之有浊。而谓无中之性则不可。又若因此而于此浊气上性。谓之见方能中则亦不可也。此处言之甚微。)
此 下教至当矣。于此两不可处。究得两可之义。则理无不通。而今日纷纭之端。不期解破而自可解破矣。盖心之本体则善。故禀得中之性。而为浊气所拘蔽而失其本体。则失其中之性而为不中之性矣。以时方不中之当体言。则谓非中之性可矣。而以元来固有之本体言。则不可谓无中之性矣。此非于其不中处言两个性也。亦非悬空而言中底性也。此如论过颡在山之水。以时方逆行之水言。则不可谓是就下之性。而以水之本体言。则不可谓无就下之性矣。孟子所以以此譬人之性善而为不善者。正取此义而其义至精矣。此盖以凡物必有本禀之体在。故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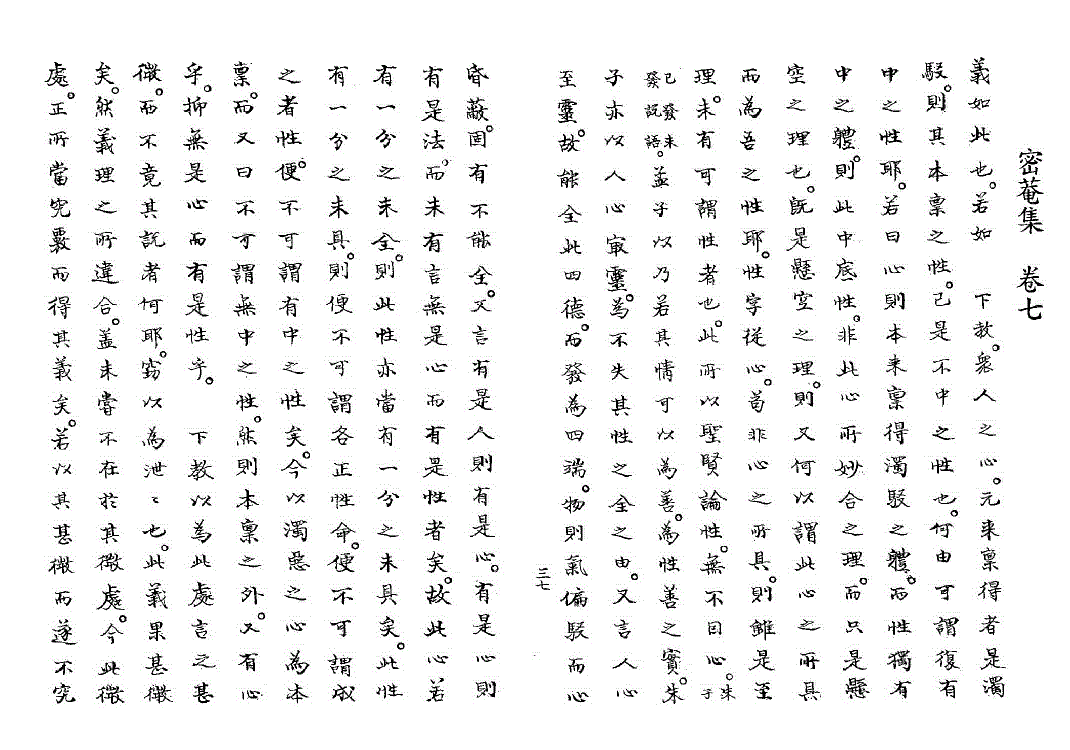 义如此也。若如 下教。众人之心。元来禀得者是浊驳。则其本禀之性。已是不中之性也。何由可谓复有中之性耶。若曰心则本来禀得浊驳之体。而性独有中之体。则此中底性。非此心所妙合之理。而只是悬空之理也。既是悬空之理。则又何以谓此心之所具而为吾之性耶。性字从心。苟非心之所具。则虽是至理。未有可谓性者也。此所以圣贤论性。无不因心。(朱子已发未发说语。)孟子以乃若其情可以为善。为性善之实。朱子亦以人心最灵。为不失其性之全之由。又言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不能全。又言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而未有言无是心而有是性者矣。故此心若有一分之未全。则此性亦当有一分之未具矣。此性有一分之未具。则便不可谓各正性命。便不可谓成之者性。便不可谓有中之性矣。今以浊恶之心为本禀。而又曰不可谓无中之性。然则本禀之外。又有心乎。抑无是心而有是性乎。 下教以为此处言之甚微。而不竟其说者何耶。窃以为泄泄也。此义果甚微矣。然义理之所违合。盖未尝不在于其微处。今此微处。正所当究覈而得其义矣。若以其甚微而遂不究
义如此也。若如 下教。众人之心。元来禀得者是浊驳。则其本禀之性。已是不中之性也。何由可谓复有中之性耶。若曰心则本来禀得浊驳之体。而性独有中之体。则此中底性。非此心所妙合之理。而只是悬空之理也。既是悬空之理。则又何以谓此心之所具而为吾之性耶。性字从心。苟非心之所具。则虽是至理。未有可谓性者也。此所以圣贤论性。无不因心。(朱子已发未发说语。)孟子以乃若其情可以为善。为性善之实。朱子亦以人心最灵。为不失其性之全之由。又言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不能全。又言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而未有言无是心而有是性者矣。故此心若有一分之未全。则此性亦当有一分之未具矣。此性有一分之未具。则便不可谓各正性命。便不可谓成之者性。便不可谓有中之性矣。今以浊恶之心为本禀。而又曰不可谓无中之性。然则本禀之外。又有心乎。抑无是心而有是性乎。 下教以为此处言之甚微。而不竟其说者何耶。窃以为泄泄也。此义果甚微矣。然义理之所违合。盖未尝不在于其微处。今此微处。正所当究覈而得其义矣。若以其甚微而遂不究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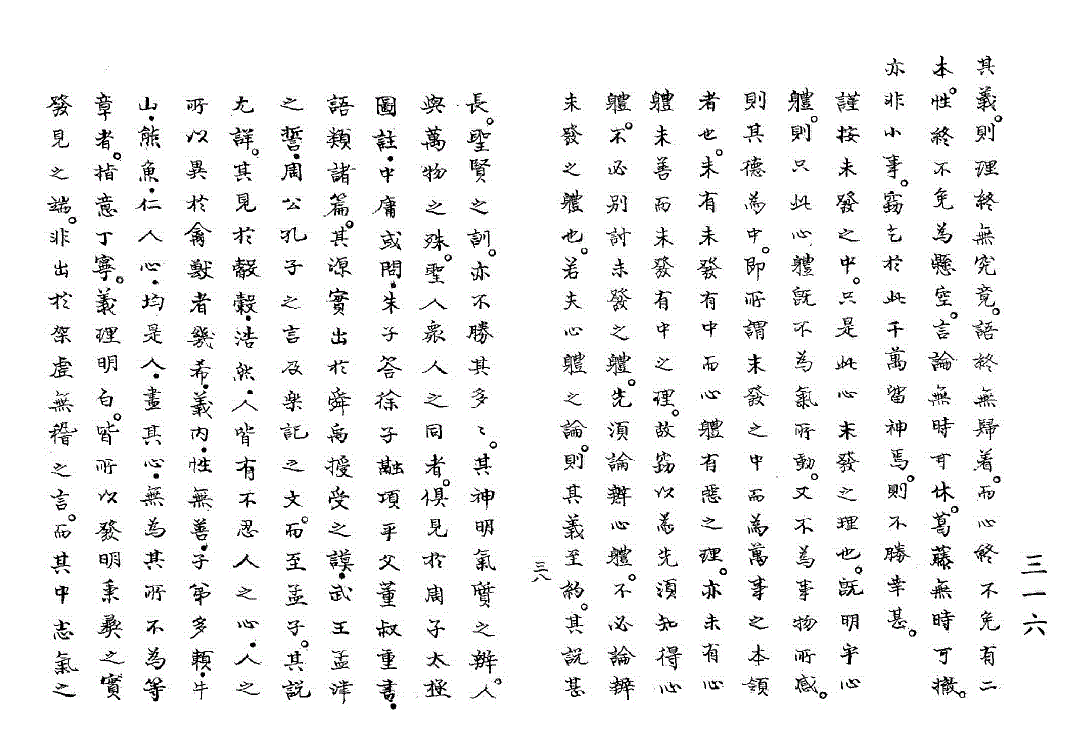 其义。则理终无究竟。语终无归着。而心终不免有二本。性终不免为悬空。言论无时可休。葛藤无时可撤。亦非小事。窃乞于此千万留神焉。则不胜幸甚。
其义。则理终无究竟。语终无归着。而心终不免有二本。性终不免为悬空。言论无时可休。葛藤无时可撤。亦非小事。窃乞于此千万留神焉。则不胜幸甚。谨按未发之中。只是此心未发之理也。既明乎心体。则只此心体既不为气所动。又不为事物所感。则其德为中。即所谓未发之中而为万事之本领者也。未有未发有中而心体有恶之理。亦未有心体未善而未发有中之理。故窃以为先须知得心体。不必别讨未发之体。先须论辨心体。不必论辨未发之体也。若夫心体之论。则其义至约。其说甚长。圣贤之训。亦不胜其多多。其神明气质之辨。人与万物之殊。圣人众人之同者。俱见于周子太极图注,中庸或问,朱子答徐子融项平父董叔重书,语类诸篇。其源实出于舜禹授受之谟,武王孟津之誓,周公孔子之言及乐记之文。而至孟子。其说尤详。其见于觳𣫎,浩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义内,性无善,子弟多赖,牛山,熊鱼,仁人心,均是人,尽其心,无为其所不为等章者。指意丁宁。义理明白。皆所以发明秉彝之实发见之端。非出于架虚无稽之言。而其中志气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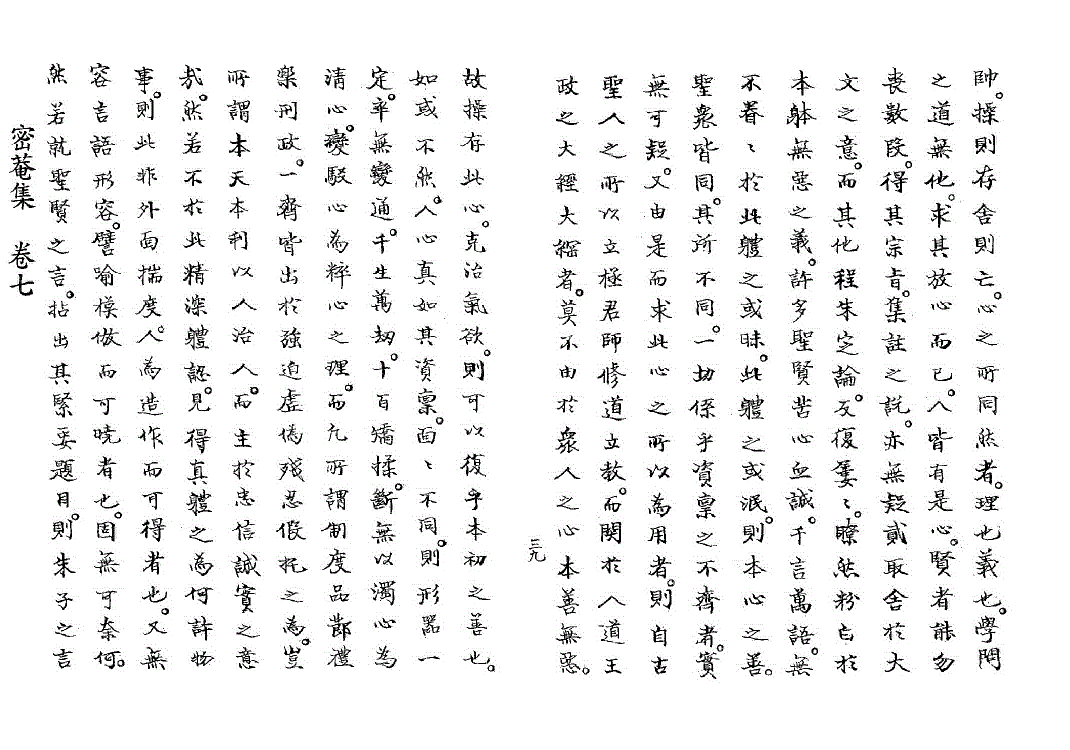 帅。操则存舍则亡。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人皆有是心。贤者能勿丧数段。得其宗旨。集注之说。亦无疑贰取舍于大文之意。而其他程朱定论。反复屡屡。瞭然粉白于本体无恶之义。许多圣贤苦心血诚。千言万语。无不眷眷于此体之或昧。此体之或泯。则本心之善。圣众皆同。其所不同。一切系乎资禀之不齐者。实无可疑。又由是而求此心之所以为用者。则自古圣人之所以立极君师修道立教。而关于人道王政之大经大纲者。莫不由于众人之心本善无恶。故操存此心。克治气欲。则可以复乎本初之善也。如或不然。人心真如其资禀。面面不同。则形器一定。卒无变通。千生万劫。十百矫揉。断无以浊心为清心。变驳心为粹心之理。而凡所谓制度品节礼乐刑政。一齐皆出于强迫虚伪残忍假托之为。岂所谓本天本利以人治人。而主于忠信诚实之意哉。然若不于此精深体认。见得真体之为何许物事。则此非外面揣度。人为造作而可得者也。又无容言语形容。譬喻模仿而可晓者也。固无可奈何。然若就圣贤之言。拈出其紧要题目。则朱子之言
帅。操则存舍则亡。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人皆有是心。贤者能勿丧数段。得其宗旨。集注之说。亦无疑贰取舍于大文之意。而其他程朱定论。反复屡屡。瞭然粉白于本体无恶之义。许多圣贤苦心血诚。千言万语。无不眷眷于此体之或昧。此体之或泯。则本心之善。圣众皆同。其所不同。一切系乎资禀之不齐者。实无可疑。又由是而求此心之所以为用者。则自古圣人之所以立极君师修道立教。而关于人道王政之大经大纲者。莫不由于众人之心本善无恶。故操存此心。克治气欲。则可以复乎本初之善也。如或不然。人心真如其资禀。面面不同。则形器一定。卒无变通。千生万劫。十百矫揉。断无以浊心为清心。变驳心为粹心之理。而凡所谓制度品节礼乐刑政。一齐皆出于强迫虚伪残忍假托之为。岂所谓本天本利以人治人。而主于忠信诚实之意哉。然若不于此精深体认。见得真体之为何许物事。则此非外面揣度。人为造作而可得者也。又无容言语形容。譬喻模仿而可晓者也。固无可奈何。然若就圣贤之言。拈出其紧要题目。则朱子之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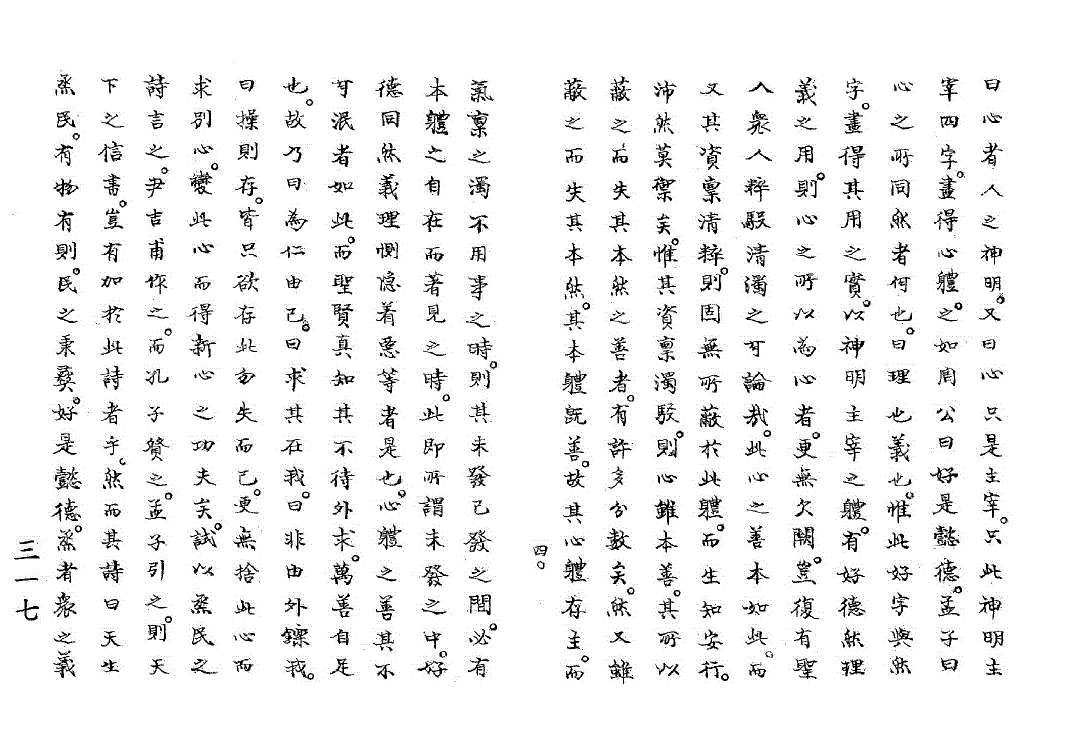 曰心者人之神明。又曰心只是主宰。只此神明主宰四字。尽得心体。之如周公曰好是懿德。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惟此好字与然字。尽得其用之实。以神明主宰之体。有好德然理义之用。则心之所以为心者。更无欠阙。岂复有圣人众人粹驳清浊之可论哉。此心之善本如此。而又其资禀清粹。则固无所蔽于此体。而生知安行。沛然莫御矣。惟其资禀浊驳。则心虽本善。其所以蔽之而失其本然之善者。有许多分数矣。然又虽蔽之而失其本然。其本体既善。故其心体存主。而气禀之浊不用事之时。则其未发已发之间。必有本体之自在而著见之时。此即所谓未发之中。好德同然义理恻隐着恶等者是也。心体之善其不可泯者如此。而圣贤真知其不待外求。万善自足也。故乃曰为仁由己。曰求其在我。曰非由外铄我。曰操则存。皆只欲存此勿失而已。更无舍此心而求别心。变此心而得新心之功夫矣。试以烝民之诗言之。尹吉甫作之。而孔子赞之。孟子引之。则天下之信书。岂有加于此诗者乎。然而其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者众之义
曰心者人之神明。又曰心只是主宰。只此神明主宰四字。尽得心体。之如周公曰好是懿德。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惟此好字与然字。尽得其用之实。以神明主宰之体。有好德然理义之用。则心之所以为心者。更无欠阙。岂复有圣人众人粹驳清浊之可论哉。此心之善本如此。而又其资禀清粹。则固无所蔽于此体。而生知安行。沛然莫御矣。惟其资禀浊驳。则心虽本善。其所以蔽之而失其本然之善者。有许多分数矣。然又虽蔽之而失其本然。其本体既善。故其心体存主。而气禀之浊不用事之时。则其未发已发之间。必有本体之自在而著见之时。此即所谓未发之中。好德同然义理恻隐着恶等者是也。心体之善其不可泯者如此。而圣贤真知其不待外求。万善自足也。故乃曰为仁由己。曰求其在我。曰非由外铄我。曰操则存。皆只欲存此勿失而已。更无舍此心而求别心。变此心而得新心之功夫矣。试以烝民之诗言之。尹吉甫作之。而孔子赞之。孟子引之。则天下之信书。岂有加于此诗者乎。然而其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者众之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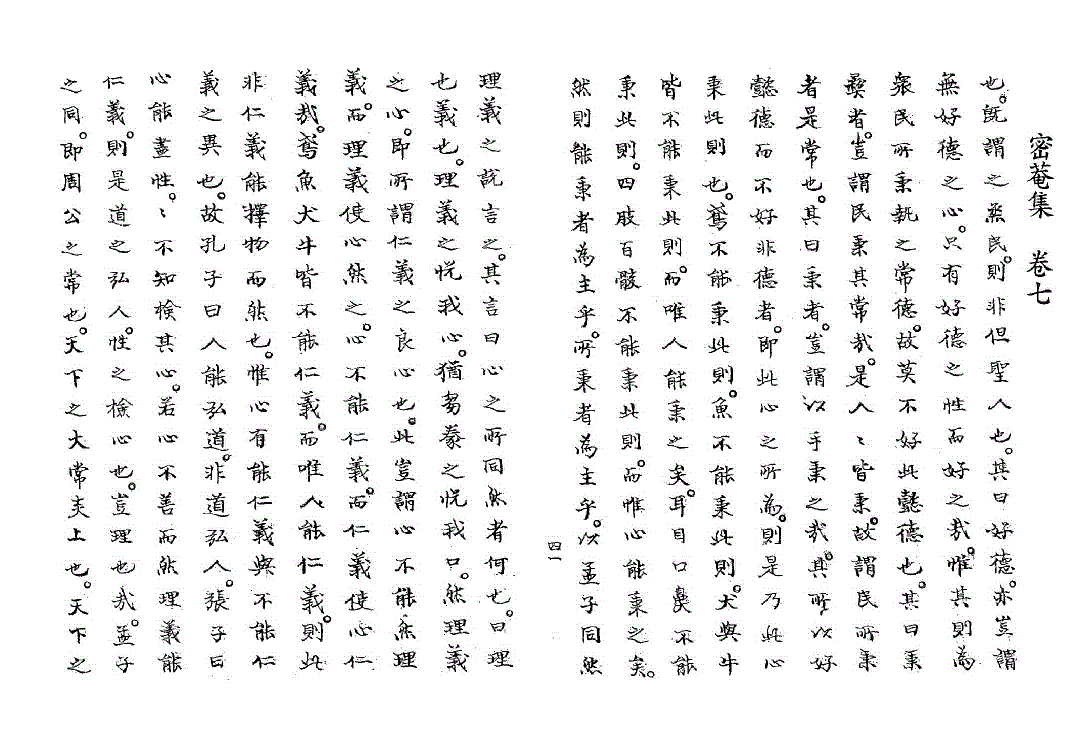 也。既谓之烝民。则非但圣人也。其曰好德。亦岂谓无好德之心。只有好德之性而好之哉。惟其则为众民所秉执之常德。故莫不好此懿德也。其曰秉彝者。岂谓民秉其常哉。是人人皆秉。故谓民所秉者是常也。其曰秉者。岂谓以手秉之哉。其所以好懿德而不好非德者。即此心之所为。则是乃此心秉此则也。鸢不能秉此则。鱼不能秉此则。犬与牛皆不能秉此则。而唯人能秉之矣。耳目口鼻不能秉此则。四肢百骸不能秉此则。而惟心能秉之矣。然则能秉者为主乎。所秉者为主乎。以孟子同然理义之说言之。其言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然理义之心。即所谓仁义之良心也。此岂谓心不能然理义。而理义使心然之。心不能仁义。而仁义使心仁义哉。鸢鱼犬牛皆不能仁义。而唯人能仁义。则此非仁义能择物而然也。惟心有能仁义与不能仁义之异也。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张子曰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若心不善而然理义能仁义。则是道之弘人。性之检心也。岂理也哉。孟子之同。即周公之常也。天下之火常炎上也。天下之
也。既谓之烝民。则非但圣人也。其曰好德。亦岂谓无好德之心。只有好德之性而好之哉。惟其则为众民所秉执之常德。故莫不好此懿德也。其曰秉彝者。岂谓民秉其常哉。是人人皆秉。故谓民所秉者是常也。其曰秉者。岂谓以手秉之哉。其所以好懿德而不好非德者。即此心之所为。则是乃此心秉此则也。鸢不能秉此则。鱼不能秉此则。犬与牛皆不能秉此则。而唯人能秉之矣。耳目口鼻不能秉此则。四肢百骸不能秉此则。而惟心能秉之矣。然则能秉者为主乎。所秉者为主乎。以孟子同然理义之说言之。其言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然理义之心。即所谓仁义之良心也。此岂谓心不能然理义。而理义使心然之。心不能仁义。而仁义使心仁义哉。鸢鱼犬牛皆不能仁义。而唯人能仁义。则此非仁义能择物而然也。惟心有能仁义与不能仁义之异也。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张子曰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若心不善而然理义能仁义。则是道之弘人。性之检心也。岂理也哉。孟子之同。即周公之常也。天下之火常炎上也。天下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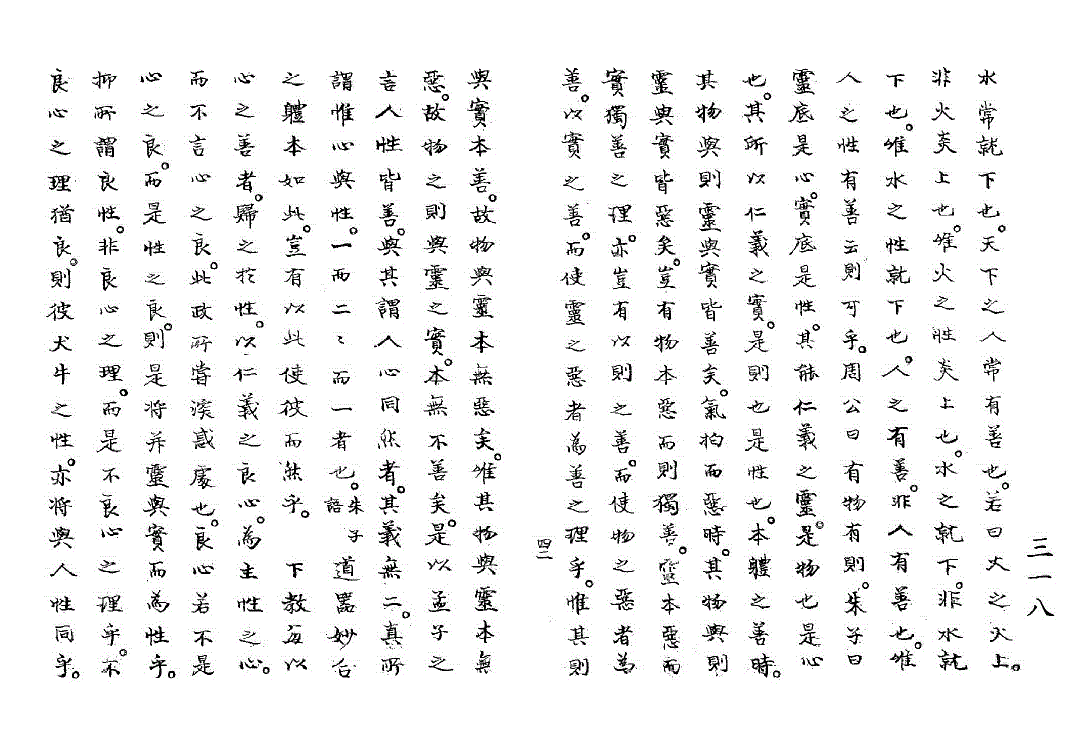 水常就下也。天下之人常有善也。若曰火之火上。非火炎上也。唯火之性炎上也。水之就下。非水就下也。唯水之性就下也。人之有善。非人有善也。唯人之性有善云则可乎。周公曰有物有则。朱子曰灵底是心。实底是性。其能仁义之灵。是物也是心也。其所以仁义之实。是则也是性也。本体之善时。其物与则灵与实皆善矣。气拘而恶时。其物与则灵与实皆恶矣。岂有物本恶而则独善。灵本恶而实独善之理。亦岂有以则之善。而使物之恶者为善。以实之善。而使灵之恶者为善之理乎。惟其则与实本善。故物与灵本无恶矣。唯其物与灵本无恶。故物之则与灵之实。本无不善矣。是以孟子之言人性皆善。与其谓人心同然者。其义无二。真所谓惟心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语)道器妙合之体本如此。岂有以此使彼而然乎。 下教每以心之善者。归之于性。以仁义之良心。为主性之心。而不言心之良。此政所尝深惑处也。良心若不是心之良。而是性之良。则是将并灵与实而为性乎。抑所谓良性。非良心之理。而是不良心之理乎。不良心之理犹良。则彼犬牛之性。亦将与人性同乎。
水常就下也。天下之人常有善也。若曰火之火上。非火炎上也。唯火之性炎上也。水之就下。非水就下也。唯水之性就下也。人之有善。非人有善也。唯人之性有善云则可乎。周公曰有物有则。朱子曰灵底是心。实底是性。其能仁义之灵。是物也是心也。其所以仁义之实。是则也是性也。本体之善时。其物与则灵与实皆善矣。气拘而恶时。其物与则灵与实皆恶矣。岂有物本恶而则独善。灵本恶而实独善之理。亦岂有以则之善。而使物之恶者为善。以实之善。而使灵之恶者为善之理乎。惟其则与实本善。故物与灵本无恶矣。唯其物与灵本无恶。故物之则与灵之实。本无不善矣。是以孟子之言人性皆善。与其谓人心同然者。其义无二。真所谓惟心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语)道器妙合之体本如此。岂有以此使彼而然乎。 下教每以心之善者。归之于性。以仁义之良心。为主性之心。而不言心之良。此政所尝深惑处也。良心若不是心之良。而是性之良。则是将并灵与实而为性乎。抑所谓良性。非良心之理。而是不良心之理乎。不良心之理犹良。则彼犬牛之性。亦将与人性同乎。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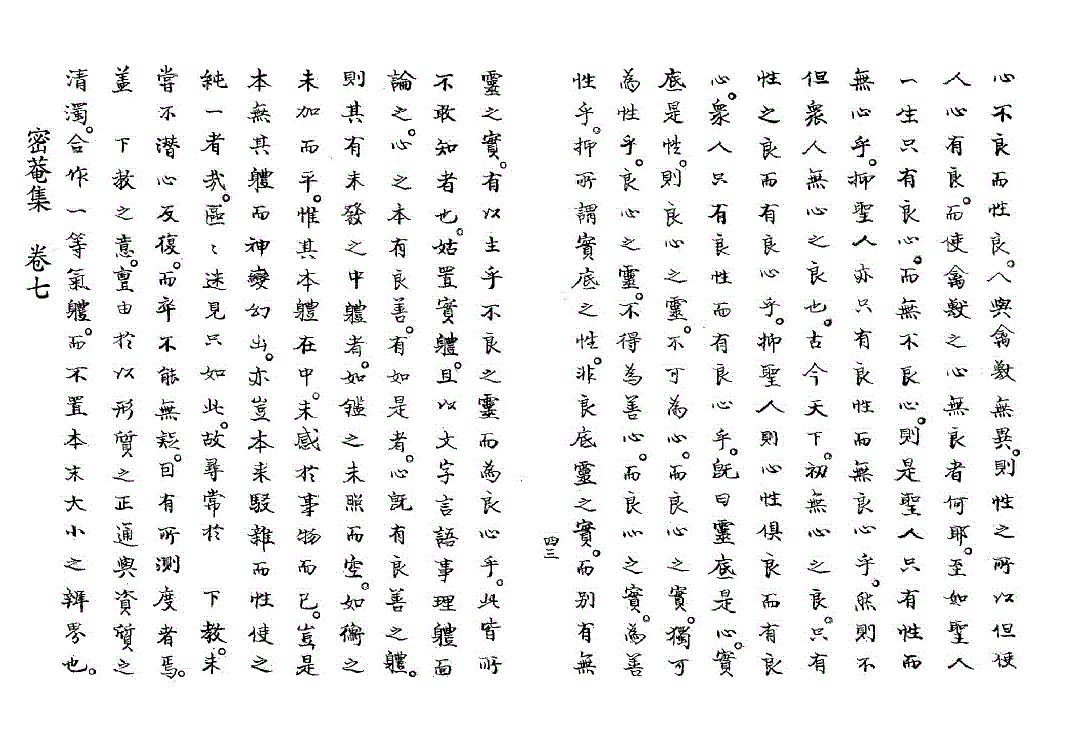 心不良而性良。人与禽兽无异。则性之所以但使人心有良。而使禽兽之心无良者何耶。至如圣人一生只有良心。而无不良心。则是圣人只有性而无心乎。抑圣人亦只有良性而无良心乎。然则不但众人无心之良也。古今天下。初无心之良。只有性之良而有良心乎。抑圣人则心性俱良而有良心。众人只有良性而有良心乎。既曰灵底是心。实底是性。则良心之灵。不可为心。而良心之实。独可为性乎。良心之灵。不得为善心。而良心之实。为善性乎。抑所谓实底之性。非良底灵之实。而别有无灵之实。有以主乎不良之灵而为良心乎。此皆所不敢知者也。姑置实体。且以文字言语事理体面论之。心之本有良善。有如是者。心既有良善之体。则其有未发之中体者。如鉴之未照而空。如衡之未加而平。惟其本体在中。未感于事物而已。岂是本无其体而神变幻出。亦岂本来驳杂而性使之纯一者哉。区区迷见只如此。故寻常于 下教。未尝不潜心反复。而卒不能无疑。因有所测度者焉。盖 下教之意。亶由于以形质之正通与资质之清浊。合作一等气体。而不置本末大小之辨界也。
心不良而性良。人与禽兽无异。则性之所以但使人心有良。而使禽兽之心无良者何耶。至如圣人一生只有良心。而无不良心。则是圣人只有性而无心乎。抑圣人亦只有良性而无良心乎。然则不但众人无心之良也。古今天下。初无心之良。只有性之良而有良心乎。抑圣人则心性俱良而有良心。众人只有良性而有良心乎。既曰灵底是心。实底是性。则良心之灵。不可为心。而良心之实。独可为性乎。良心之灵。不得为善心。而良心之实。为善性乎。抑所谓实底之性。非良底灵之实。而别有无灵之实。有以主乎不良之灵而为良心乎。此皆所不敢知者也。姑置实体。且以文字言语事理体面论之。心之本有良善。有如是者。心既有良善之体。则其有未发之中体者。如鉴之未照而空。如衡之未加而平。惟其本体在中。未感于事物而已。岂是本无其体而神变幻出。亦岂本来驳杂而性使之纯一者哉。区区迷见只如此。故寻常于 下教。未尝不潜心反复。而卒不能无疑。因有所测度者焉。盖 下教之意。亶由于以形质之正通与资质之清浊。合作一等气体。而不置本末大小之辨界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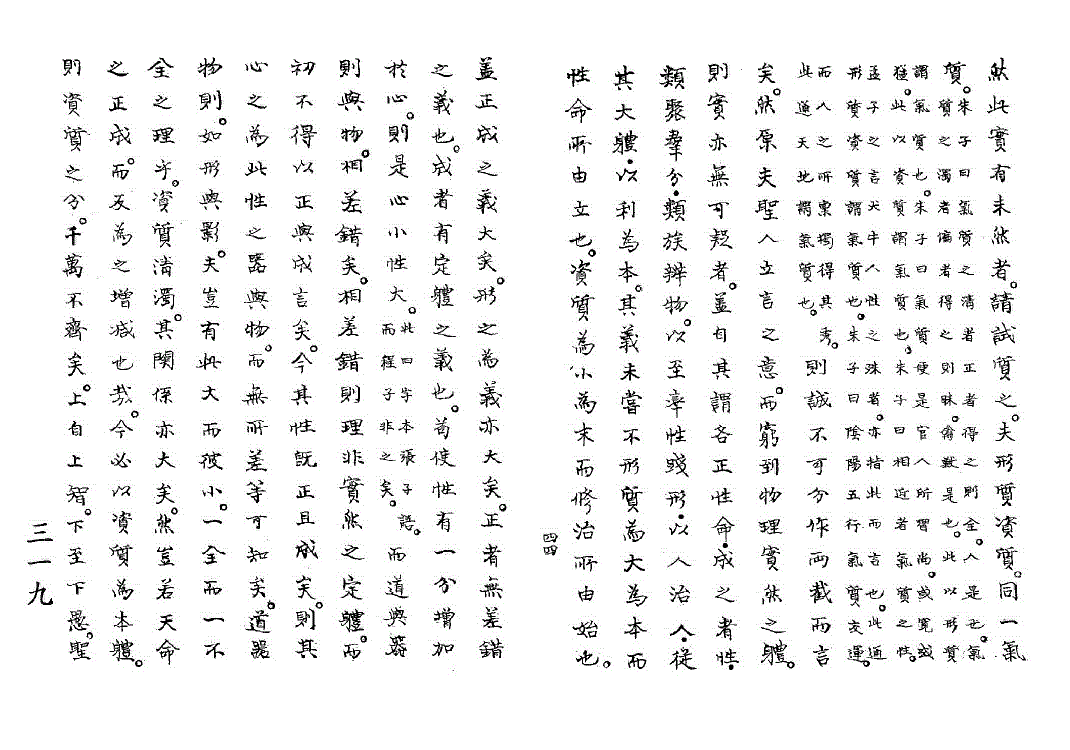 然此实有未然者。请试质之。夫形质资质。同一气质。(朱子曰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此以形质谓气质也。朱子曰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此以资质谓气质也。朱子曰相近者气质之性。孟子之言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此通形质资质谓气质也。朱子曰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此通天地谓气质也。)则诚不可分作两截而言矣。然原夫圣人立言之意。而穷到物理实然之体。则实亦无可疑者。盖自其谓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类聚群分,类族辨物。以至率性践形,以人治人,从其大体,以利为本。其义未尝不形质为大为本而性命所由立也。资质为小为末而修治所由始也。盖正成之义大矣。形之为义亦大矣。正者无差错之义也。成者有定体之义也。苟使性有一分增加于心。则是心小性大。(此四字本张子语。而程子非之矣。)而道与器则与物。相差错矣。相差错则理非实然之定体。而初不得以正与成言矣。今其性既正且成矣。则其心之为此性之器与物。而无所差等可知矣。道器物则。如形与影。夫岂有此大而彼小。一全而一不全之理乎。资质清浊。其关系亦大矣。然岂若天命之正成。而反为之增减也哉。今必以资质为本体。则资质之分。千万不齐矣。上自上智。下至下愚。圣
然此实有未然者。请试质之。夫形质资质。同一气质。(朱子曰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此以形质谓气质也。朱子曰气质便是官人所习尚。或宽或猛。此以资质谓气质也。朱子曰相近者气质之性。孟子之言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此通形质资质谓气质也。朱子曰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此通天地谓气质也。)则诚不可分作两截而言矣。然原夫圣人立言之意。而穷到物理实然之体。则实亦无可疑者。盖自其谓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类聚群分,类族辨物。以至率性践形,以人治人,从其大体,以利为本。其义未尝不形质为大为本而性命所由立也。资质为小为末而修治所由始也。盖正成之义大矣。形之为义亦大矣。正者无差错之义也。成者有定体之义也。苟使性有一分增加于心。则是心小性大。(此四字本张子语。而程子非之矣。)而道与器则与物。相差错矣。相差错则理非实然之定体。而初不得以正与成言矣。今其性既正且成矣。则其心之为此性之器与物。而无所差等可知矣。道器物则。如形与影。夫岂有此大而彼小。一全而一不全之理乎。资质清浊。其关系亦大矣。然岂若天命之正成。而反为之增减也哉。今必以资质为本体。则资质之分。千万不齐矣。上自上智。下至下愚。圣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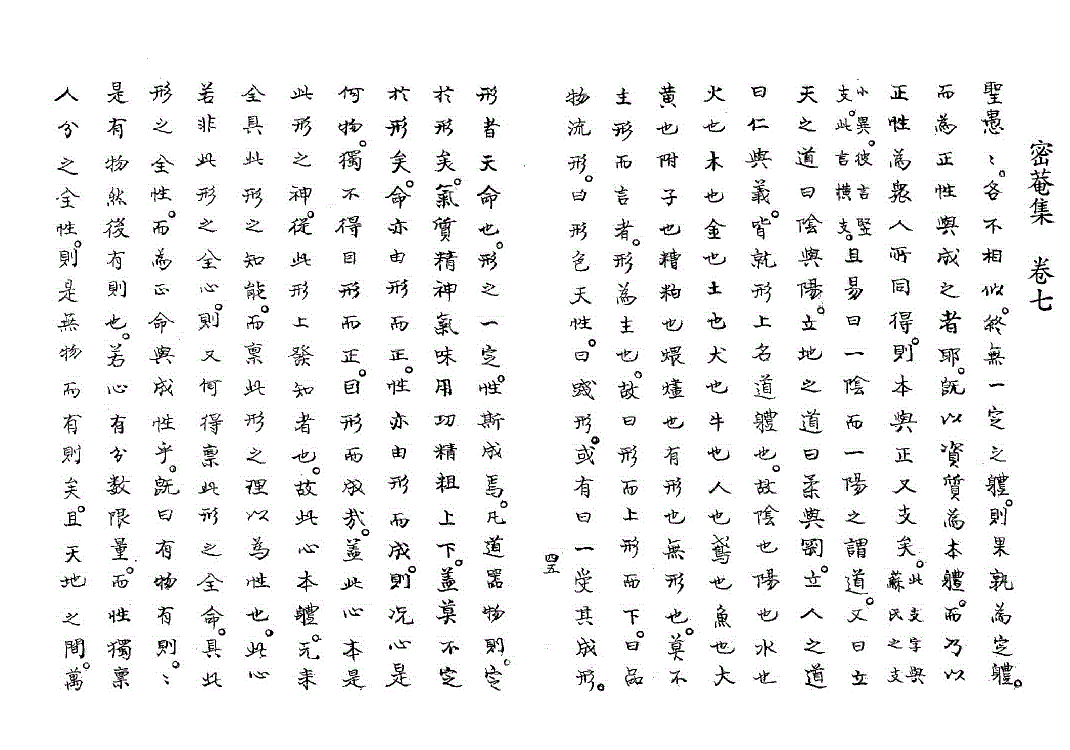 圣愚愚。各不相似。终无一定之体。则果孰为定体。而为正性与成之者耶。既以资质为本体。而乃以正性为众人所同得。则本与正又支矣。(此支字与苏氏之支小异。彼言竖支。此言横支。)且易曰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皆就形上名道体也。故阴也阳也水也火也木也金也土也犬也牛也人也鸢也鱼也大黄也附子也糟粕也煨烬也有形也无形也。莫不主形而言者。形为主也。故曰形而上形而下。曰品物流形。曰形色天性。曰践形。或有曰一受其成形。形者天命也。形之一定。性斯成焉。凡道器物则。定于形矣。气质精神气味用功精粗上下。盖莫不定于形矣。命亦由形而正。性亦由形而成。则况心是何物。独不得因形而正。因形而成哉。盖此心本是此形之神。从此形上发知者也。故此心本体。元来全具此形之知能。而禀此形之理以为性也。此心若非此形之全心。则又何得禀此形之全命。具此形之全性。而为正命与成性乎。既曰有物有则。则是有物然后有则也。若心有分数限量。而性独禀人分之全性。则是无物而有则矣。且天地之间。万
圣愚愚。各不相似。终无一定之体。则果孰为定体。而为正性与成之者耶。既以资质为本体。而乃以正性为众人所同得。则本与正又支矣。(此支字与苏氏之支小异。彼言竖支。此言横支。)且易曰一阴而一阳之谓道。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皆就形上名道体也。故阴也阳也水也火也木也金也土也犬也牛也人也鸢也鱼也大黄也附子也糟粕也煨烬也有形也无形也。莫不主形而言者。形为主也。故曰形而上形而下。曰品物流形。曰形色天性。曰践形。或有曰一受其成形。形者天命也。形之一定。性斯成焉。凡道器物则。定于形矣。气质精神气味用功精粗上下。盖莫不定于形矣。命亦由形而正。性亦由形而成。则况心是何物。独不得因形而正。因形而成哉。盖此心本是此形之神。从此形上发知者也。故此心本体。元来全具此形之知能。而禀此形之理以为性也。此心若非此形之全心。则又何得禀此形之全命。具此形之全性。而为正命与成性乎。既曰有物有则。则是有物然后有则也。若心有分数限量。而性独禀人分之全性。则是无物而有则矣。且天地之间。万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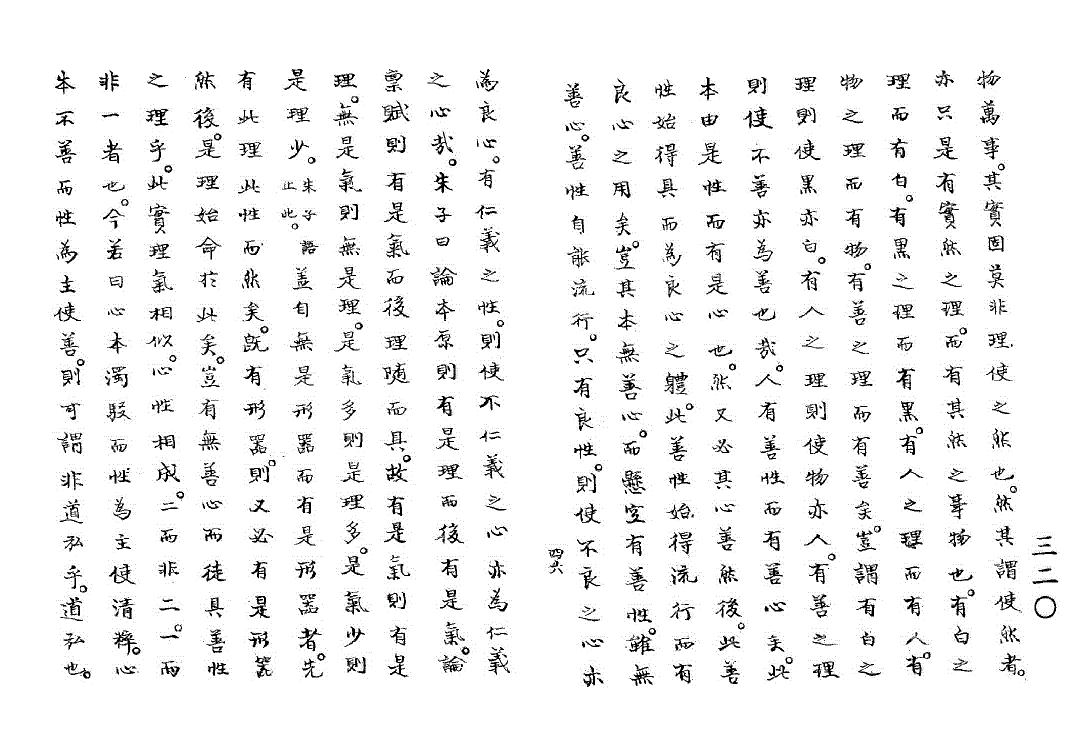 物万事。其实固莫非理使之然也。然其谓使然者。亦只是有实然之理。而有其然之事物也。有白之理而有白。有黑之理而有黑。有人之理而有人。有物之理而有物。有善之理而有善矣。岂谓有白之理则使黑亦白。有人之理则使物亦人。有善之理则使不善亦为善也哉。人有善性而有善心矣。此本由是性而有是心也。然又必其心善然后。此善性始得具而为良心之体。此善性始得流行而有良心之用矣。岂其本无善心。而悬空有善性。虽无善心。善性自能流行。只有良性。则使不良之心亦为良心。有仁义之性。则使不仁义之心亦为仁义之心哉。朱子曰论本原则有是理而后有是气。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朱子语止此。)盖自无是形器而有是形器者。先有此理此性而然矣。既有形器。则又必有是形器然后。是理始命于此矣。岂有无善心而徒具善性之理乎。此实理气相似。心性相成。二而非二。一而非一者也。今若曰心本浊驳而性为主使清粹。心本不善而性为主使善。则可谓非道弘乎。道弘也。
物万事。其实固莫非理使之然也。然其谓使然者。亦只是有实然之理。而有其然之事物也。有白之理而有白。有黑之理而有黑。有人之理而有人。有物之理而有物。有善之理而有善矣。岂谓有白之理则使黑亦白。有人之理则使物亦人。有善之理则使不善亦为善也哉。人有善性而有善心矣。此本由是性而有是心也。然又必其心善然后。此善性始得具而为良心之体。此善性始得流行而有良心之用矣。岂其本无善心。而悬空有善性。虽无善心。善性自能流行。只有良性。则使不良之心亦为良心。有仁义之性。则使不仁义之心亦为仁义之心哉。朱子曰论本原则有是理而后有是气。论禀赋则有是气而后理随而具。故有是气则有是理。无是气则无是理。是气多则是理多。是气少则是理少。(朱子语止此。)盖自无是形器而有是形器者。先有此理此性而然矣。既有形器。则又必有是形器然后。是理始命于此矣。岂有无善心而徒具善性之理乎。此实理气相似。心性相成。二而非二。一而非一者也。今若曰心本浊驳而性为主使清粹。心本不善而性为主使善。则可谓非道弘乎。道弘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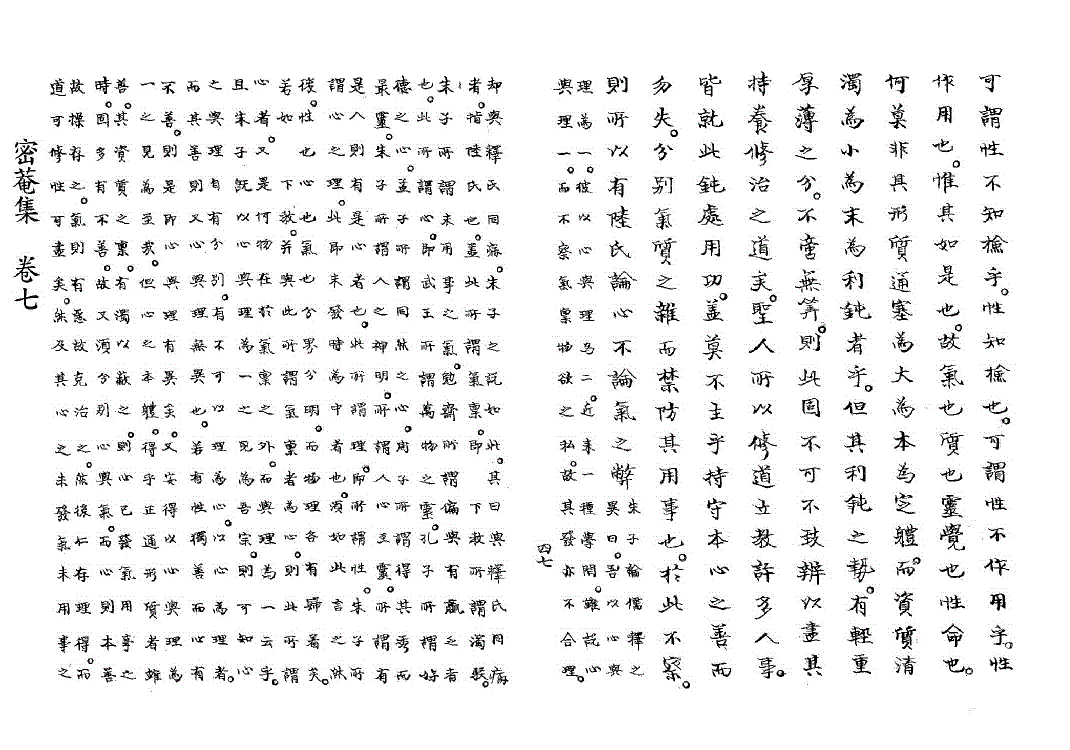 可谓性不知检乎。性知检也。可谓性不作用乎。性作用也。惟其如是也。故气也质也灵觉也性命也。何莫非其形质通塞为大为本为定体。而质质清浊为小为末为利钝者乎。但其利钝之势。有轻重厚薄之分。不啻无算。则此固不可不致辨以尽其持养修治之道矣。圣人所以修道立教许多人事。皆就此钝处用功。盖莫不主乎持守本心之善而勿失。分别气质之杂而禁防其用事也。于此不察。则所以有陆氏论心不论气之弊(朱子论儒释之异曰。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近来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朱子之说如此。其曰与释氏同病者。指陆氏也。盖此所谓气禀。即 下教所谓浊驳。朱子所谓未用事之气。勉斋所谓偏与有赢乏者也。此所谓心。即武王所谓万物之灵。孔子所谓好德之心。孟子所谓同然之心。周子所谓得其秀而最灵。朱子所谓人之神明。所谓人心至灵。所谓有是人则有是心者也。此所谓理。即所谓性。朱子所谓心之理。此即未发时为中者也。须如此言之然后。性也心也气也分界分明。而物理各有归着矣。若如 下教。并与此所谓气禀者为心。则此所谓心者。又是何物在于气禀之外。而与理为一云乎。且朱子既以心与理为一之见为吾宗。则可知心之与理自有分别。有不可以理为心。以心为理者。而其善则又心与理无异也。若有性独善而心有不善。则是即心与理有异矣。又安得以心与理为一之见为至哉。但心之本体。得乎正通形质者虽善。其资质之禀。有浊以蔽之。则心已发气用事之时。固多有不善。故又须分别心与气。而心则本善故操存之。气则有恶故克治之。然后仁存理得。而道可修性可尽矣。然及其心之未发气未用事之
可谓性不知检乎。性知检也。可谓性不作用乎。性作用也。惟其如是也。故气也质也灵觉也性命也。何莫非其形质通塞为大为本为定体。而质质清浊为小为末为利钝者乎。但其利钝之势。有轻重厚薄之分。不啻无算。则此固不可不致辨以尽其持养修治之道矣。圣人所以修道立教许多人事。皆就此钝处用功。盖莫不主乎持守本心之善而勿失。分别气质之杂而禁防其用事也。于此不察。则所以有陆氏论心不论气之弊(朱子论儒释之异曰。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近来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朱子之说如此。其曰与释氏同病者。指陆氏也。盖此所谓气禀。即 下教所谓浊驳。朱子所谓未用事之气。勉斋所谓偏与有赢乏者也。此所谓心。即武王所谓万物之灵。孔子所谓好德之心。孟子所谓同然之心。周子所谓得其秀而最灵。朱子所谓人之神明。所谓人心至灵。所谓有是人则有是心者也。此所谓理。即所谓性。朱子所谓心之理。此即未发时为中者也。须如此言之然后。性也心也气也分界分明。而物理各有归着矣。若如 下教。并与此所谓气禀者为心。则此所谓心者。又是何物在于气禀之外。而与理为一云乎。且朱子既以心与理为一之见为吾宗。则可知心之与理自有分别。有不可以理为心。以心为理者。而其善则又心与理无异也。若有性独善而心有不善。则是即心与理有异矣。又安得以心与理为一之见为至哉。但心之本体。得乎正通形质者虽善。其资质之禀。有浊以蔽之。则心已发气用事之时。固多有不善。故又须分别心与气。而心则本善故操存之。气则有恶故克治之。然后仁存理得。而道可修性可尽矣。然及其心之未发气未用事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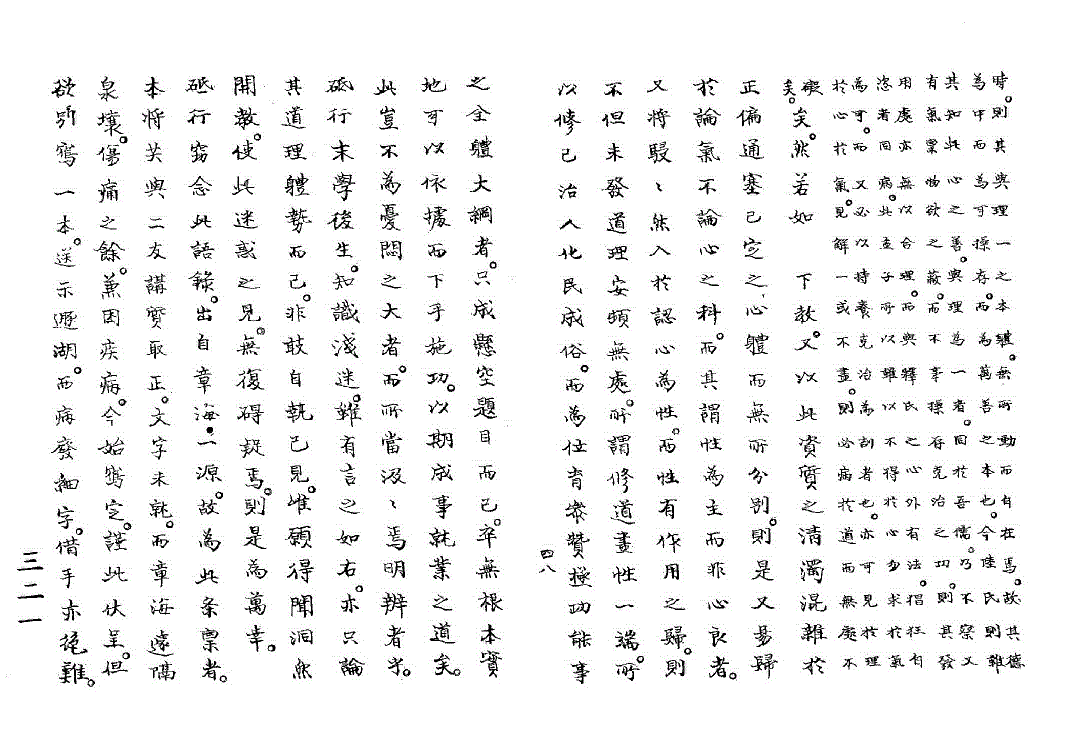 时。则其与理一之本体。无所动而自在焉。故其德为中而为可操存。而为万善之本也。今陆氏则虽其知此心之善。与理为一者。同于吾儒。乃不察又有气禀物欲之蔽。而不事操存克治之功。则其发用处亦无以合理。而与释氏之心外有法。猖狂自恣者同病。此孟子所以虽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为可。而又必以持养克治为训者也。亦可见于理于心于气。见解一或不尽。则必病于道而无处不碍矣。)矣。然若如 下教。又以此资质之清浊混杂于正偏通塞已定之心体而无所分别。则是又易归于论气不论心之科。而其谓性为主而非心良者。又将骎骎然入于认心为性。而性有作用之归。则不但未发道理安顿无处。所谓修道尽性一端。所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而为位育参赞极功能事之全体大纲者。只成悬空题目而已。卒无根本实地可以依据而下手施功。以期成事就业之道矣。此岂不为忧闷之大者。而所当汲汲焉明辨者乎。砥行末学后生。知识浅迷。虽有言之如右。亦只论其道理体势而已。非敢自执己见。唯愿得闻洞然开教。使此迷惑之见。无复碍疑焉。则是为万幸。
时。则其与理一之本体。无所动而自在焉。故其德为中而为可操存。而为万善之本也。今陆氏则虽其知此心之善。与理为一者。同于吾儒。乃不察又有气禀物欲之蔽。而不事操存克治之功。则其发用处亦无以合理。而与释氏之心外有法。猖狂自恣者同病。此孟子所以虽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为可。而又必以持养克治为训者也。亦可见于理于心于气。见解一或不尽。则必病于道而无处不碍矣。)矣。然若如 下教。又以此资质之清浊混杂于正偏通塞已定之心体而无所分别。则是又易归于论气不论心之科。而其谓性为主而非心良者。又将骎骎然入于认心为性。而性有作用之归。则不但未发道理安顿无处。所谓修道尽性一端。所以修己治人化民成俗。而为位育参赞极功能事之全体大纲者。只成悬空题目而已。卒无根本实地可以依据而下手施功。以期成事就业之道矣。此岂不为忧闷之大者。而所当汲汲焉明辨者乎。砥行末学后生。知识浅迷。虽有言之如右。亦只论其道理体势而已。非敢自执己见。唯愿得闻洞然开教。使此迷惑之见。无复碍疑焉。则是为万幸。砥行窃念此语录。出自章海,一源。故为此条禀者。本将共与二友讲质取正。文字未就。而章海遽隔泉壤。伤痛之馀。兼困疾病。今始写定。谨此伏呈。但欲别写一本。送示遁湖。而病废细字。借手亦绝难。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3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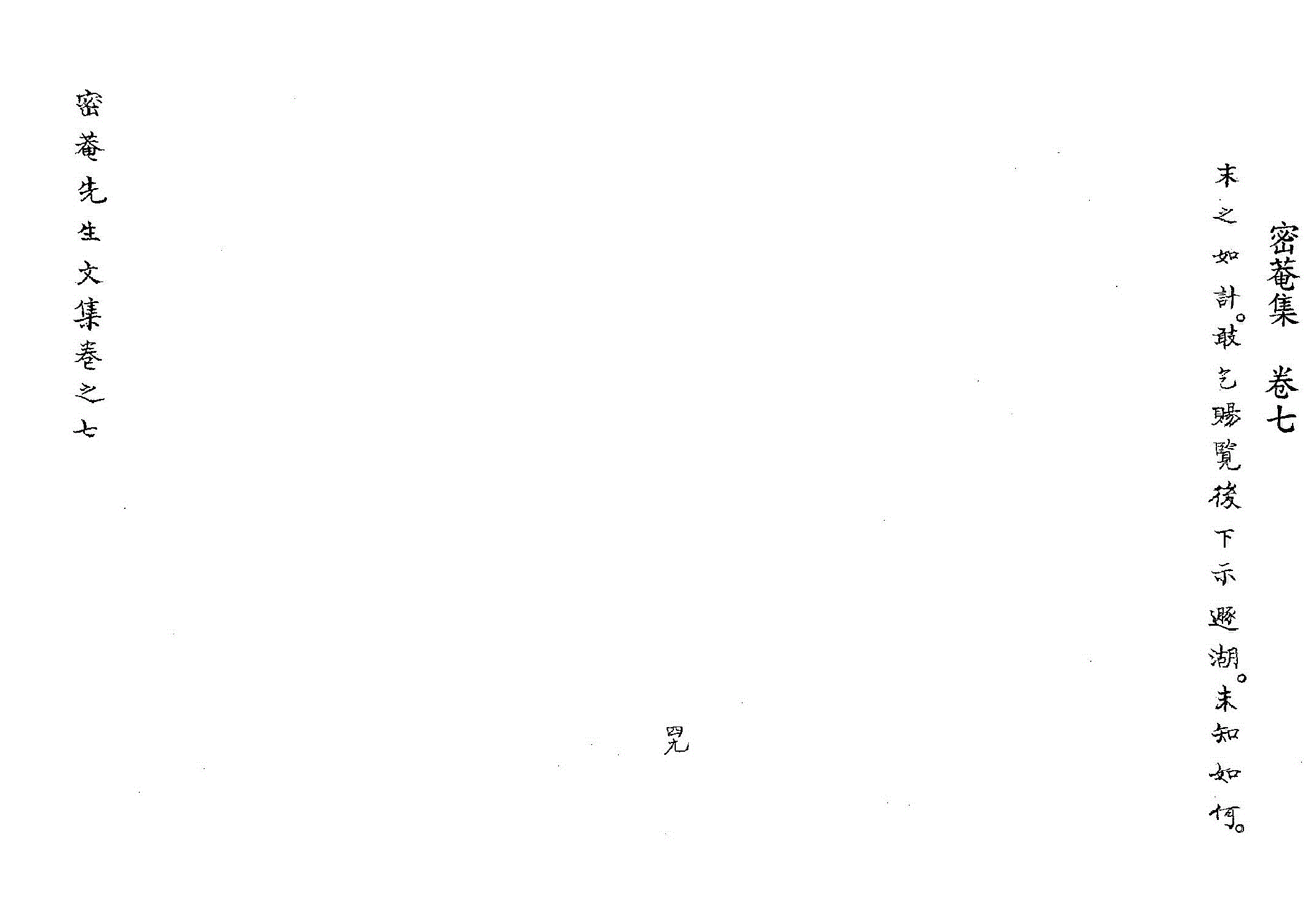 末之如计。敢乞赐览后下示遁湖。未知如何。
末之如计。敢乞赐览后下示遁湖。未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