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书
书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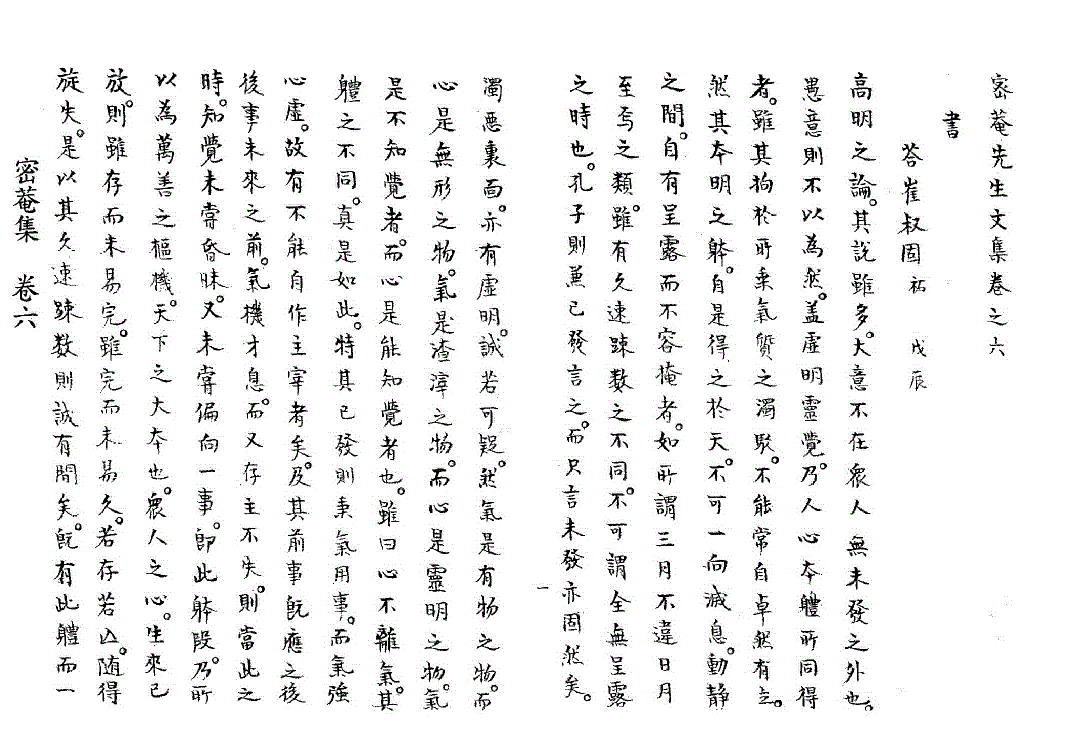 答崔叔固(祏○戊辰)
答崔叔固(祏○戊辰)高明之论。其说虽多。大意不在众人无未发之外也。愚意则不以为然。盖虚明灵觉。乃人心本体所同得者。虽其拘于所乘气质之浊驳。不能常自卓然有立。然其本明之体。自是得之于天。不可一向灭息。动静之间。自有呈露而不容掩者。如所谓三月不违日月至焉之类。虽有久速疏数之不同。不可谓全无呈露之时也。孔子则兼已发言之。而只言未发亦固然矣。浊恶里面。亦有虚明。诚若可疑。然气是有物之物。而心是无形之物。气是渣滓之物。而心是灵明之物。气是不知觉者。而心是能知觉者也。虽曰心不离气。其体之不同。真是如此。特其已发则秉气用事。而气强心虚。故有不能自作主宰者矣。及其前事既应之后后事未来之前。气机才息。而又存主不失。则当此之时。知觉未尝昏昧。又未尝偏向一事。即此体段。乃所以为万善之枢机。天下之大本也。众人之心。生来已放。则虽存而未易完。虽完而未易久。若存若亡。随得旋失。是以其久速疏数则诚有间矣。既有此体而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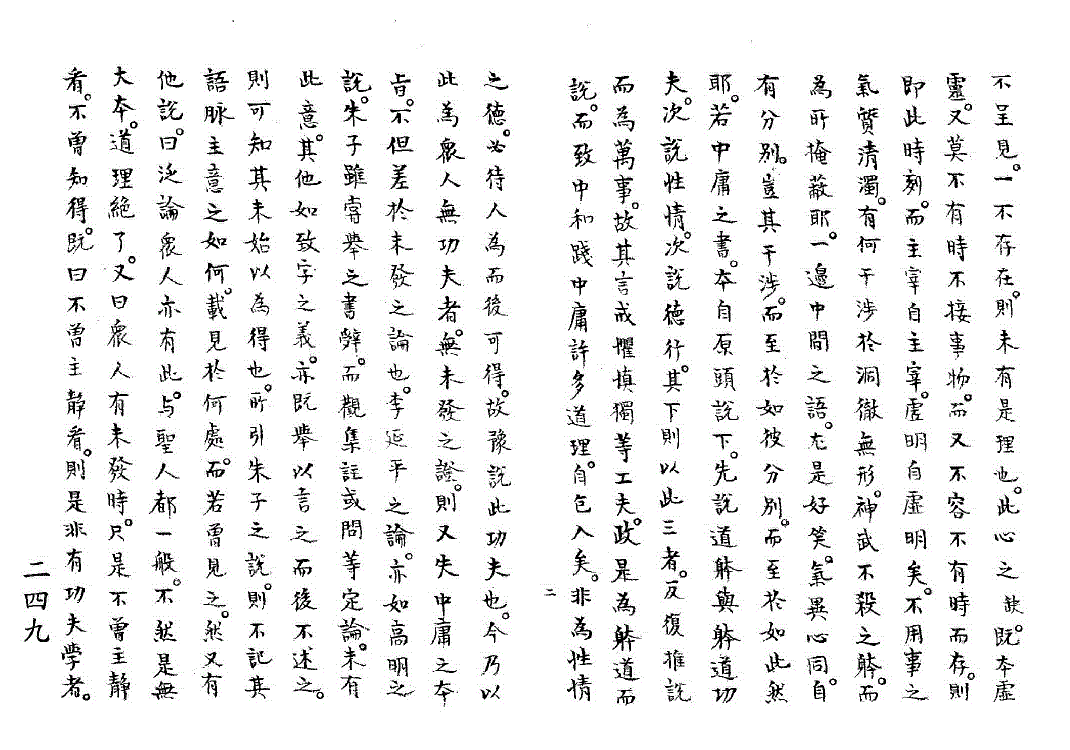 不呈见。一不存在。则未有是理也。此心之(缺)。既本虚灵。又莫不有时不接事物。而又不容不有时而存。则即此时刻。而主宰自主宰。虚明自虚明矣。不用事之气质清浊。有何干涉于洞彻无形。神武不杀之体。而为所掩蔽耶。一边中间之语。尤是好笑。气异心同。自有分别。岂其干涉。而至于如彼分别。而至于如此然耶。若中庸之书。本自原头说下。先说道体与体道功夫。次说性情。次说德行。其下则以此三者。反复推说而为万事。故其言戒惧慎独等工夫。政是为体道而说。而致中和践中庸许多道理。自包入矣。非为性情之德。必待人为而后可得。故豫说此功夫也。今乃以此为众人无功夫者。无未发之證。则又失中庸之本旨。不但差于未发之论也。李延平之论。亦如高明之说。朱子虽尝举之书辞。而观集注或问等定论。未有此意。其他如致字之义。亦既举以言之而后不述之。则可知其未始以为得也。所引朱子之说。则不记其语脉主意之如何。载见于何处。而若曾见之。然又有他说。曰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又曰众人有未发时。只是不曾主静看。不曾知得。既曰不曾主静看。则是非有功夫学者。
不呈见。一不存在。则未有是理也。此心之(缺)。既本虚灵。又莫不有时不接事物。而又不容不有时而存。则即此时刻。而主宰自主宰。虚明自虚明矣。不用事之气质清浊。有何干涉于洞彻无形。神武不杀之体。而为所掩蔽耶。一边中间之语。尤是好笑。气异心同。自有分别。岂其干涉。而至于如彼分别。而至于如此然耶。若中庸之书。本自原头说下。先说道体与体道功夫。次说性情。次说德行。其下则以此三者。反复推说而为万事。故其言戒惧慎独等工夫。政是为体道而说。而致中和践中庸许多道理。自包入矣。非为性情之德。必待人为而后可得。故豫说此功夫也。今乃以此为众人无功夫者。无未发之證。则又失中庸之本旨。不但差于未发之论也。李延平之论。亦如高明之说。朱子虽尝举之书辞。而观集注或问等定论。未有此意。其他如致字之义。亦既举以言之而后不述之。则可知其未始以为得也。所引朱子之说。则不记其语脉主意之如何。载见于何处。而若曾见之。然又有他说。曰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又曰众人有未发时。只是不曾主静看。不曾知得。既曰不曾主静看。则是非有功夫学者。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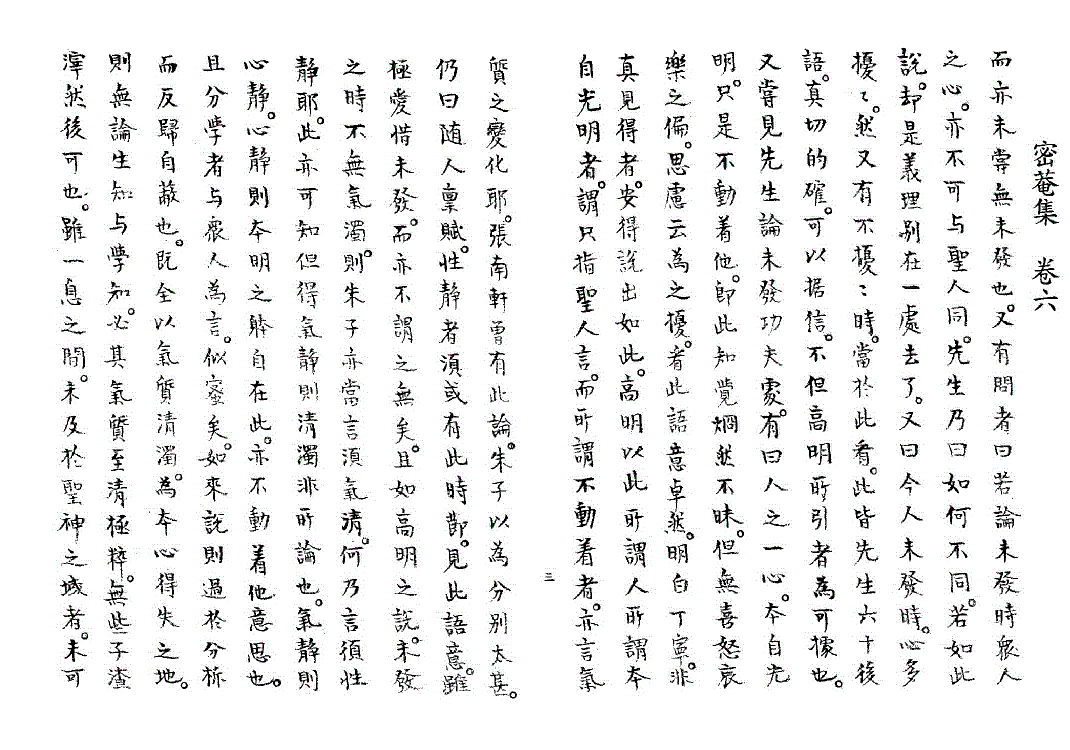 而亦未尝无未发也。又有问者曰若论未发时众人之心。亦不可与圣人同。先生乃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义理别在一处去了。又曰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此皆先生六十后语。真切的确。可以据信。不但高明所引者为可据也。又尝见先生论未发功夫处。有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只是不动着他。即此知觉烱然不昧。但无喜怒哀乐之偏。思虑云为之扰。看此语意卓然。明白丁宁。非真见得者。安得说出如此。高明以此所谓人所谓本自光明者。谓只指圣人言。而所谓不动着者。亦言气质之变化耶。张南轩曾有此论。朱子以为分别太甚。仍曰随人禀赋。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见此语意。虽极爱惜未发。而亦不谓之无矣。且如高明之说。未发之时不无气浊。则朱子亦当言须气清。何乃言须性静耶。此亦可知但得气静则清浊非所论也。气静则心静。心静则本明之体自在此。亦不动着他意思也。且分学者与众人为言。似蜜矣。如来说则过于分析而反归自蔽也。既全以气质清浊。为本心得失之地。则无论生知与学知。必其气质至清极粹。无些子渣滓然后可也。虽一息之间。未及于圣神之域者。未可
而亦未尝无未发也。又有问者曰若论未发时众人之心。亦不可与圣人同。先生乃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说。却是义理别在一处去了。又曰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此皆先生六十后语。真切的确。可以据信。不但高明所引者为可据也。又尝见先生论未发功夫处。有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只是不动着他。即此知觉烱然不昧。但无喜怒哀乐之偏。思虑云为之扰。看此语意卓然。明白丁宁。非真见得者。安得说出如此。高明以此所谓人所谓本自光明者。谓只指圣人言。而所谓不动着者。亦言气质之变化耶。张南轩曾有此论。朱子以为分别太甚。仍曰随人禀赋。性静者须或有此时节。见此语意。虽极爱惜未发。而亦不谓之无矣。且如高明之说。未发之时不无气浊。则朱子亦当言须气清。何乃言须性静耶。此亦可知但得气静则清浊非所论也。气静则心静。心静则本明之体自在此。亦不动着他意思也。且分学者与众人为言。似蜜矣。如来说则过于分析而反归自蔽也。既全以气质清浊。为本心得失之地。则无论生知与学知。必其气质至清极粹。无些子渣滓然后可也。虽一息之间。未及于圣神之域者。未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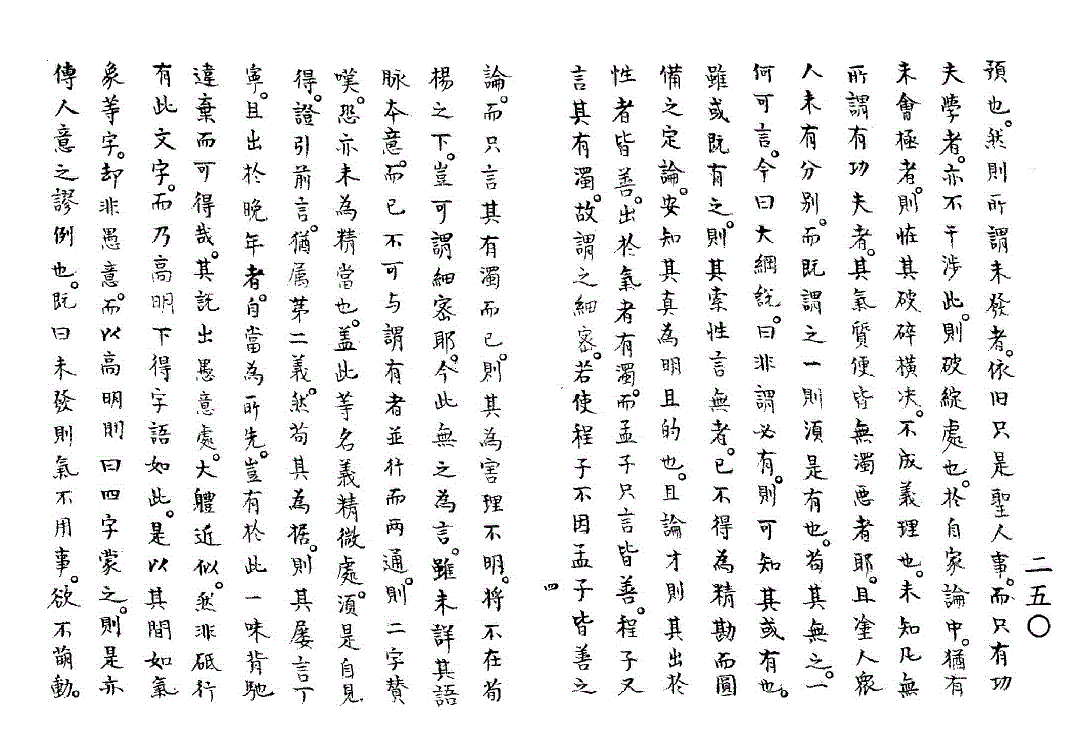 预也。然则所谓未发者。依旧只是圣人事。只有功夫学者。亦不干涉此。则破绽处也。于自家论中。犹有未会极者。则怪其破碎横决。不成义理也。未知凡无所谓有功夫者。其气质便皆无浊恶者耶。且涂人众人未有分别。而既谓之一则须是有也。苟其无之。一何可言。今曰大纲说。曰非谓必有。则可知其或有也。虽或既有之。则其索性言无者。已不得为精勘而圆备之定论。安知其真为明且的也。且论才则其出于性者皆善。出于气者有浊。而孟子只言皆善。程子又言其有浊。故谓之细密。若使程子不因孟子皆善之论。而只言其有浊而已。则其为害理不明。将不在荀杨之下。岂可谓细密耶。今此无之为言。虽未详其语脉本意。而已不可与谓有者并行而两通。则二字赞叹。恐亦未为精当也。盖此等名义精微处。须是自见得。證引前言。犹属第二义。然苟其为据。则其屡言丁宁。且出于晚年者。自当为所先。岂有于此一味背驰违弃而可得哉。其说出愚意处。大体近似。然非砥行有此文字。而乃高明下得字语如此。是以其间如气象等字。却非愚意。而以高明则曰四字蒙之。则是亦传人意之谬例也。既曰未发则气不用事。欲不萌动。
预也。然则所谓未发者。依旧只是圣人事。只有功夫学者。亦不干涉此。则破绽处也。于自家论中。犹有未会极者。则怪其破碎横决。不成义理也。未知凡无所谓有功夫者。其气质便皆无浊恶者耶。且涂人众人未有分别。而既谓之一则须是有也。苟其无之。一何可言。今曰大纲说。曰非谓必有。则可知其或有也。虽或既有之。则其索性言无者。已不得为精勘而圆备之定论。安知其真为明且的也。且论才则其出于性者皆善。出于气者有浊。而孟子只言皆善。程子又言其有浊。故谓之细密。若使程子不因孟子皆善之论。而只言其有浊而已。则其为害理不明。将不在荀杨之下。岂可谓细密耶。今此无之为言。虽未详其语脉本意。而已不可与谓有者并行而两通。则二字赞叹。恐亦未为精当也。盖此等名义精微处。须是自见得。證引前言。犹属第二义。然苟其为据。则其屡言丁宁。且出于晚年者。自当为所先。岂有于此一味背驰违弃而可得哉。其说出愚意处。大体近似。然非砥行有此文字。而乃高明下得字语如此。是以其间如气象等字。却非愚意。而以高明则曰四字蒙之。则是亦传人意之谬例也。既曰未发则气不用事。欲不萌动。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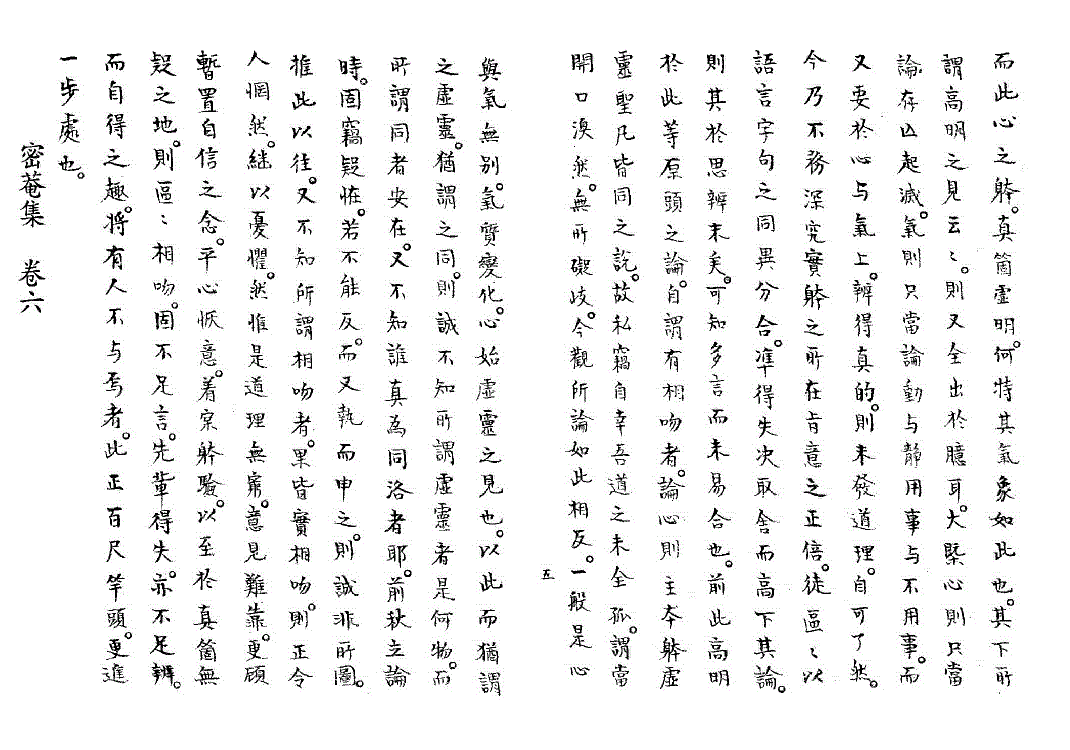 而此心之体。真个虚明。何特其气象如此也。其下所谓高明之见云云。则又全出于臆耳。大槩心则只当论存亡起灭。气则只当论动与静用事与不用事。而又要于心与气上。辨得真的。则未发道理。自可了然。今乃不务深究实体之所在旨意之正倍。徒区区以语言字句之同异分合。准得失决取舍而高下其论。则其于思辨末矣。可知多言而未易合也。前此高明于此等原头之论。自谓有相吻者。论心则主本体虚灵圣凡皆同之说。故私窃自幸吾道之未全孤。谓当开口涣然。无所碍岐。今观所论如此相反。一般是心与气无别。气质变化。心始虚灵之见也。以此而犹谓之虚灵。犹谓之同。则诚不知所谓虚灵者是何物。而所谓同者安在。又不知谁真为同洛者耶。前秋立论时。固窃疑怪。若不能反。而又执而申之。则诚非所图。推此以往。又不知所谓相吻者。果皆实相吻。则正令人惘然。继以忧惧。然惟是道理无穷。意见难靠。更顾暂置自信之念。平心恢意。着宲体验。以至于真个无疑之地。则区区相吻。固不足言。先辈得失。亦不足辨。而自得之趣。将有人不与焉者。此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处也。
而此心之体。真个虚明。何特其气象如此也。其下所谓高明之见云云。则又全出于臆耳。大槩心则只当论存亡起灭。气则只当论动与静用事与不用事。而又要于心与气上。辨得真的。则未发道理。自可了然。今乃不务深究实体之所在旨意之正倍。徒区区以语言字句之同异分合。准得失决取舍而高下其论。则其于思辨末矣。可知多言而未易合也。前此高明于此等原头之论。自谓有相吻者。论心则主本体虚灵圣凡皆同之说。故私窃自幸吾道之未全孤。谓当开口涣然。无所碍岐。今观所论如此相反。一般是心与气无别。气质变化。心始虚灵之见也。以此而犹谓之虚灵。犹谓之同。则诚不知所谓虚灵者是何物。而所谓同者安在。又不知谁真为同洛者耶。前秋立论时。固窃疑怪。若不能反。而又执而申之。则诚非所图。推此以往。又不知所谓相吻者。果皆实相吻。则正令人惘然。继以忧惧。然惟是道理无穷。意见难靠。更顾暂置自信之念。平心恢意。着宲体验。以至于真个无疑之地。则区区相吻。固不足言。先辈得失。亦不足辨。而自得之趣。将有人不与焉者。此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处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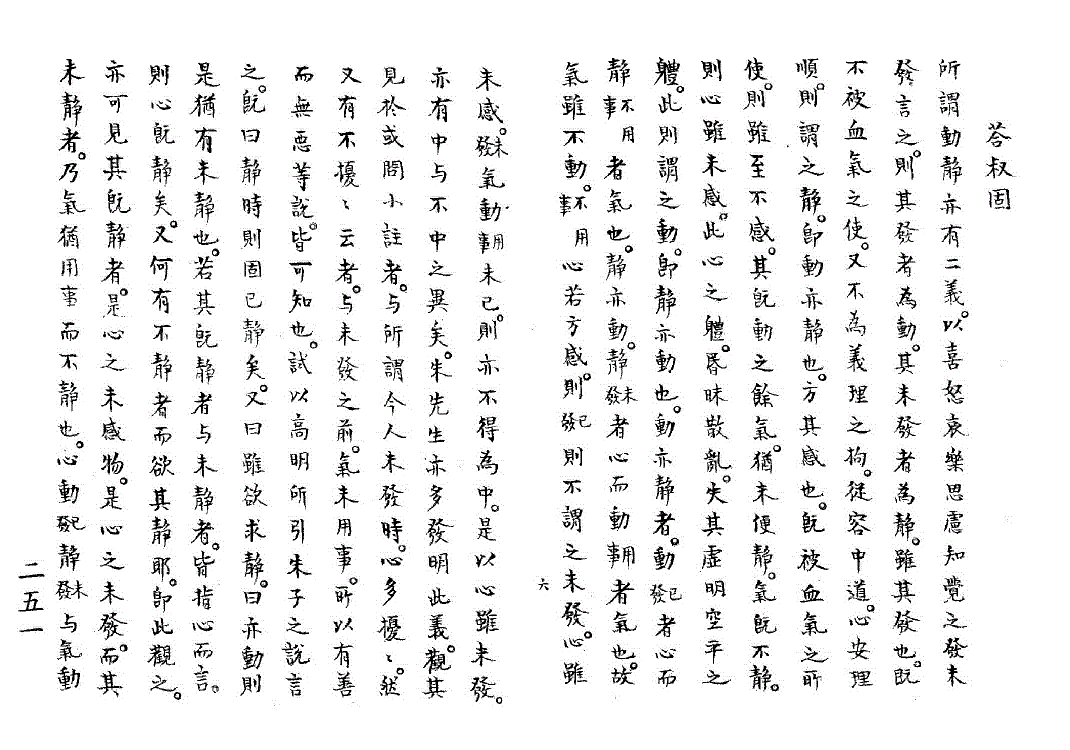 答叔固
答叔固所谓动静亦有二义。以喜怒哀乐思虑知觉之发未发言之。则其发者为动。其未发者为静。虽其发也。既不被血气之使。又不为义理之拘。从容中道。心安理顺。则谓之静。即动亦静也。方其感也。既被血气之所使。则虽至不感。其既动之馀气。犹未便静。气既不静。则心虽未感。此心之体。昏昧散乱。失其虚明空平之体。此则谓之动。即静亦动也。动亦静者。动(已发)者心而静(不用事)者气也。静亦动。静(未发)者心而动(用事)者气也。故气虽不动。(不用事)心若方感。则(已发)则不谓之未发。心虽未感。(未发)气动(用事)未已。则亦不得为中。是以心虽未发。亦有中与不中之异矣。朱先生亦多发明此义。观其见于或问小注者。与所谓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云者。与未发之前。气未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恶等说。皆可知也。试以高明所引朱子之说言之。既曰静时则固已静矣。又曰虽欲求静。曰亦动则是犹有未静也。若其既静者与未静者。皆指心而言。则心既静矣。又何有不静者而欲其静耶。即此观之。亦可见其既静者。是心之未感物。是心之未发。而其未静者。乃气犹用事而不静也。心动(已发)静(未发)与气动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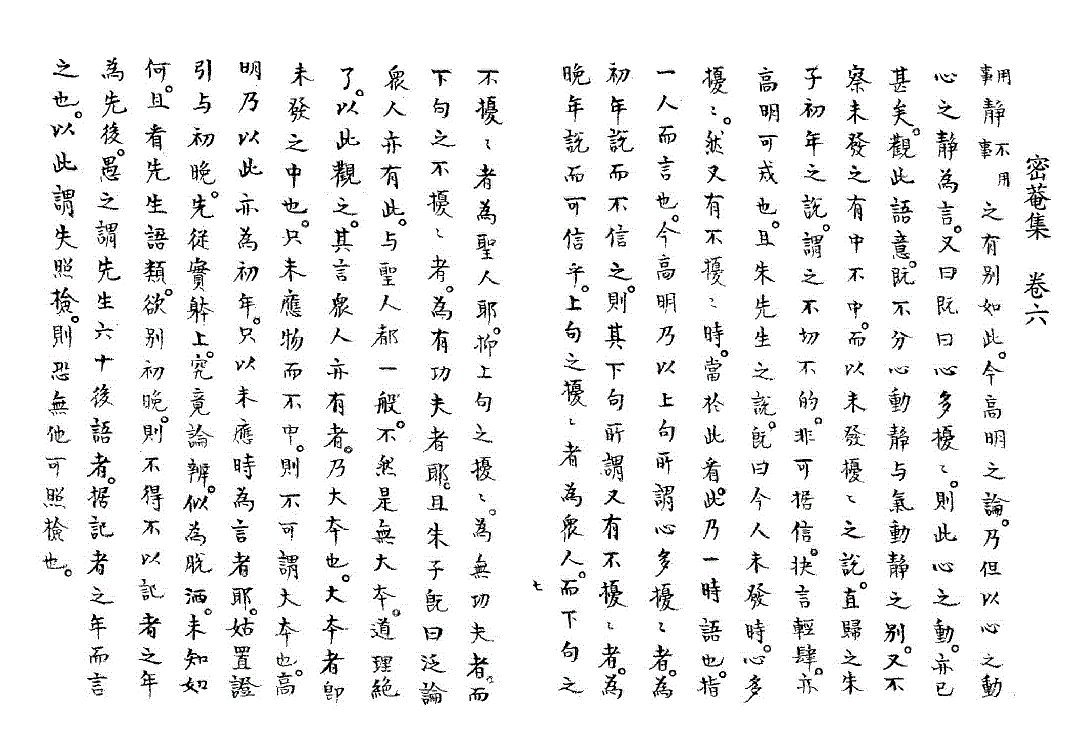 (用事)静(不用事)之有别如此。今高明之论。乃但以心之动心之静为言。又曰既曰心多扰扰。则此心之动。亦已甚矣。观此语意。既不分心动静与气动静之别。又不察未发之有中不中。而以未发扰扰之说。直归之朱子初年之说。谓之不切不的。非可据信。快言轻肆。亦高明可戒也。且朱先生之说。既曰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此乃一时语也。指一人而言也。今高明乃以上句所谓心多扰扰者。为初年说而不信之。则其下句所谓又有不扰扰者。为晚年说而可信乎。上句之扰扰者为众人。而下句之不扰扰者为圣人耶。抑上句之扰扰。为无功夫者。而下句之不扰扰者。为有功夫者耶。且朱子既曰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以此观之。其言众人亦有者。乃大本也。大本者即未发之中也。只未应物而不中。则不可谓大本也。高明乃以此亦为初年。只以未应时为言者耶。姑置證引与初晚。先从实体上。究竟论辨。似为脱洒。未知如何。且看先生语类。欲别初晚。则不得不以记者之年为先后。愚之谓先生六十后语者。据记者之年而言之也。以此谓失照检。则恐无他可照检也。
(用事)静(不用事)之有别如此。今高明之论。乃但以心之动心之静为言。又曰既曰心多扰扰。则此心之动。亦已甚矣。观此语意。既不分心动静与气动静之别。又不察未发之有中不中。而以未发扰扰之说。直归之朱子初年之说。谓之不切不的。非可据信。快言轻肆。亦高明可戒也。且朱先生之说。既曰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时。当于此看。此乃一时语也。指一人而言也。今高明乃以上句所谓心多扰扰者。为初年说而不信之。则其下句所谓又有不扰扰者。为晚年说而可信乎。上句之扰扰者为众人。而下句之不扰扰者为圣人耶。抑上句之扰扰。为无功夫者。而下句之不扰扰者。为有功夫者耶。且朱子既曰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以此观之。其言众人亦有者。乃大本也。大本者即未发之中也。只未应物而不中。则不可谓大本也。高明乃以此亦为初年。只以未应时为言者耶。姑置證引与初晚。先从实体上。究竟论辨。似为脱洒。未知如何。且看先生语类。欲别初晚。则不得不以记者之年为先后。愚之谓先生六十后语者。据记者之年而言之也。以此谓失照检。则恐无他可照检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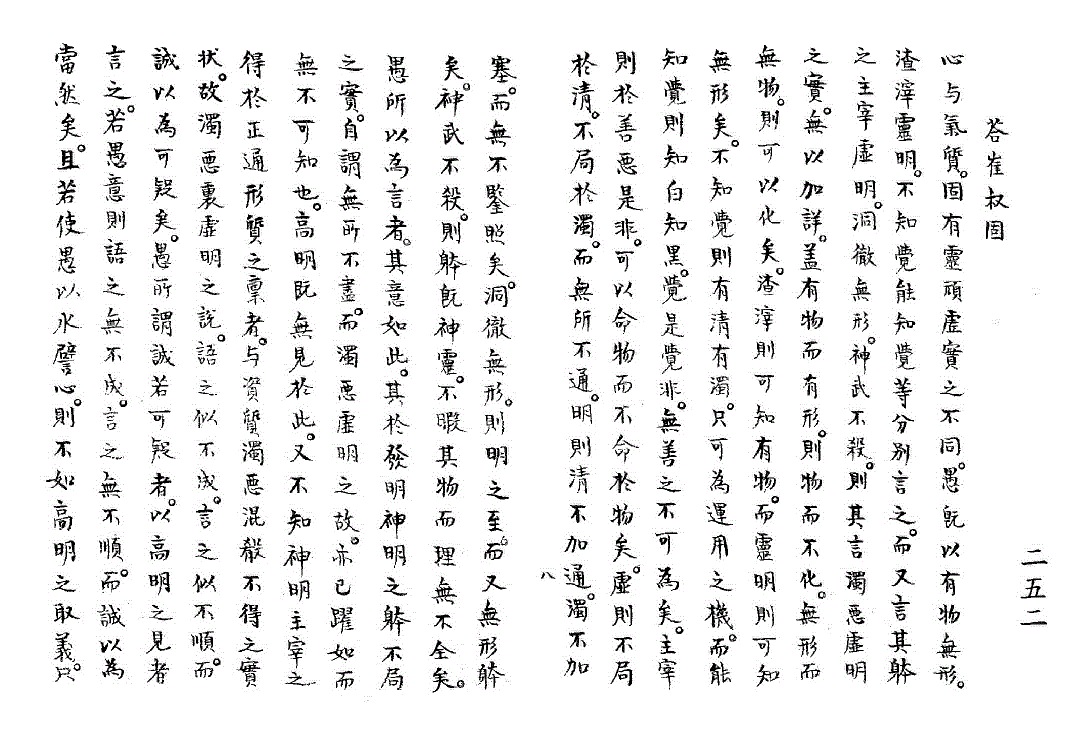 答崔叔固
答崔叔固心与气质。固有灵顽虚实之不同。愚既以有物无形。渣滓灵明。不知觉能知觉等分别言之。而又言其体之主宰虚明。洞彻无形。神武不杀。则其言浊恶虚明之实。无以加详。盖有物而有形。则物而不化。无形而无物。则可以化矣。渣滓则可知有物。而灵明则可知无形矣。不知觉则有清有浊。只可为运用之机。而能知觉则知白知黑。觉是觉非。无善之不可为矣。主宰则于善恶是非。可以命物而不命于物矣。虚则不局于清。不局于浊。而无所不通。明则清不加通。浊不加塞。而无不鉴照矣。洞彻无形。则明之至。而又无形体矣。神武不杀。则体既神灵。不暇其物而理无不全矣。愚所以为言者。其意如此。其于发明神明之体不局之实。自谓无所不尽。而浊恶虚明之故。亦已跃如而无不可知也。高明既无见于此。又不知神明主宰之得于正通形质之禀者。与资质浊恶混殽不得之实状。故浊恶里虚明之说。语之似不成。言之似不顺。而诚以为可疑矣。愚所谓诚若可疑者。以高明之见者言之。若愚意则语之无不成。言之无不顺。而诚以为当然矣。且若使愚以水譬心。则不如高明之取义。只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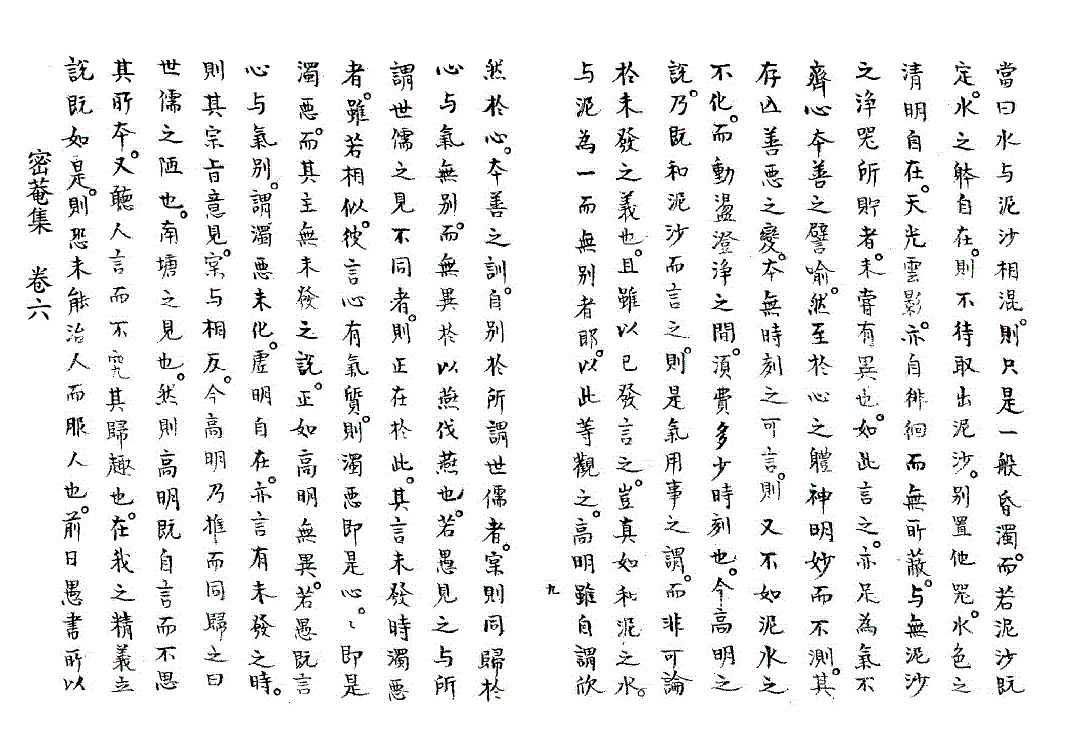 当曰水与泥沙相混。则只是一般昏浊。而若泥沙既定。水之体自在。则不待取出泥沙。别置他器。水色之清明自在。天光云影。亦自徘徊而无所蔽。与无泥沙之净器所贮者。未尝有异也。如此言之。亦足为气不齐心本善之譬喻。然至于心之体神明妙而不测。其存亡善恶之变。本无时刻之可言。则又不如泥水之不化。而动荡澄净之间。须费多少时刻也。今高明之说。乃既和泥沙而言之。则是气用事之谓。而非可论于未发之义也。且虽以已发言之。岂真如和泥之水。与泥为一而无别者耶。以此等观之。高明虽自谓欣然于心。本善之训。自别于所谓世儒者。宲则同归于心与气无别。而无异于以燕伐燕也。若愚见之与所谓世儒之见不同者。则正在于此。其言未发时浊恶者。虽若相似。彼言心有气质。则浊恶即是心。心即是浊恶。而其主无未发之说。正如高明无异。若愚既言心与气别。谓浊恶未化。虚明自在。亦言有未发之时。则其宗旨意见。宲与相反。今高明乃推而同归之曰世儒之陋也。南塘之见也。然则高明既自言而不思其所本。又听人言而不究其归趣也。在我之精义立说既如是。则恐未能治人而服人也。前日愚书所以
当曰水与泥沙相混。则只是一般昏浊。而若泥沙既定。水之体自在。则不待取出泥沙。别置他器。水色之清明自在。天光云影。亦自徘徊而无所蔽。与无泥沙之净器所贮者。未尝有异也。如此言之。亦足为气不齐心本善之譬喻。然至于心之体神明妙而不测。其存亡善恶之变。本无时刻之可言。则又不如泥水之不化。而动荡澄净之间。须费多少时刻也。今高明之说。乃既和泥沙而言之。则是气用事之谓。而非可论于未发之义也。且虽以已发言之。岂真如和泥之水。与泥为一而无别者耶。以此等观之。高明虽自谓欣然于心。本善之训。自别于所谓世儒者。宲则同归于心与气无别。而无异于以燕伐燕也。若愚见之与所谓世儒之见不同者。则正在于此。其言未发时浊恶者。虽若相似。彼言心有气质。则浊恶即是心。心即是浊恶。而其主无未发之说。正如高明无异。若愚既言心与气别。谓浊恶未化。虚明自在。亦言有未发之时。则其宗旨意见。宲与相反。今高明乃推而同归之曰世儒之陋也。南塘之见也。然则高明既自言而不思其所本。又听人言而不究其归趣也。在我之精义立说既如是。则恐未能治人而服人也。前日愚书所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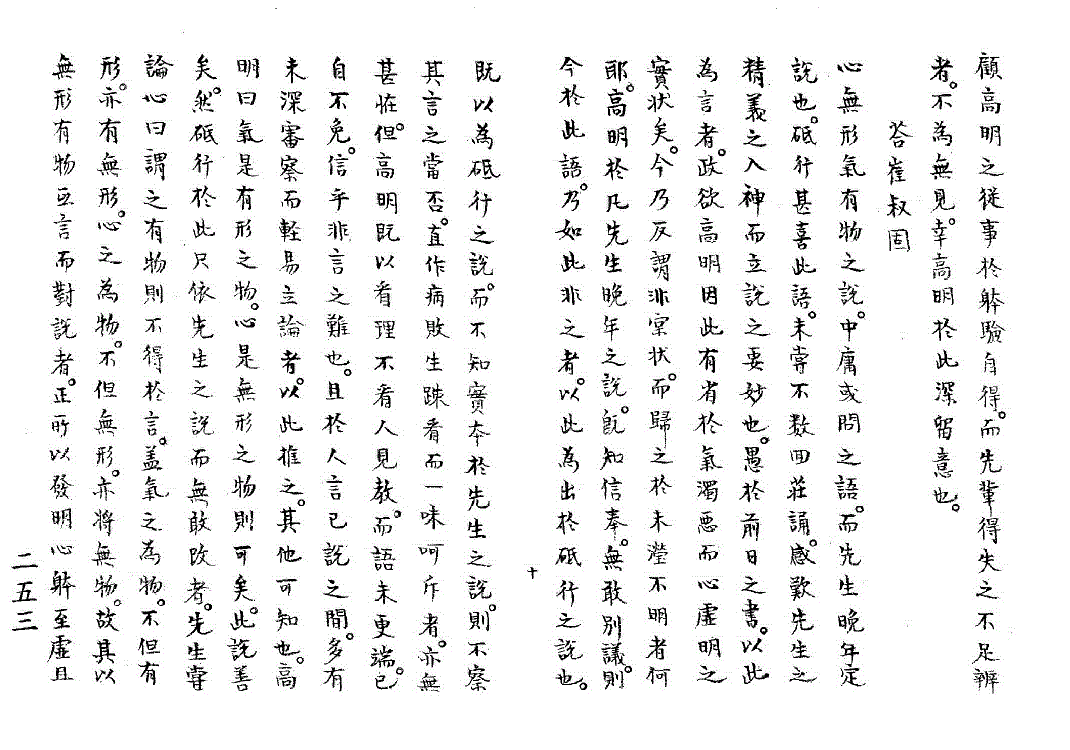 顾高明之从事于体验自得。而先辈得失之不足辨者。不为无见。幸高明于此深留意也。
顾高明之从事于体验自得。而先辈得失之不足辨者。不为无见。幸高明于此深留意也。答崔叔固
心无形气有物之说。中庸或问之语。而先生晚年定说也。砥行甚喜此语。未尝不数回庄诵。感叹先生之精义之入神而立说之要妙也。愚于前日之书。以此为言者。政欲高明因此有省于气浊恶而心虚明之实状矣。今乃反谓非宲状。而归之于未滢不明者何耶。高明于凡先生晚年之说。既知信奉。无敢别议。则今于此语。乃如此非之者。以此为出于砥行之说也。既以为砥行之说。而不知实本于先生之说。则不察其言之当否。直作病败生疏看而一味呵斥者。亦无甚怪。但高明既以看理不看人见教。而语未更端。已自不免。信乎非言之难也。且于人言己说之间。多有未深审察而轻易立论者。以此推之。其他可知也。高明曰气是有形之物。心是无形之物则可矣。此说善矣。然砥行于此只依先生之说而无敢改者。先生尝论心曰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盖气之为物。不但有形。亦有无形。心之为物。不但无形。亦将无物。故其以无形有物互言而对说者。正所以发明心体至虚且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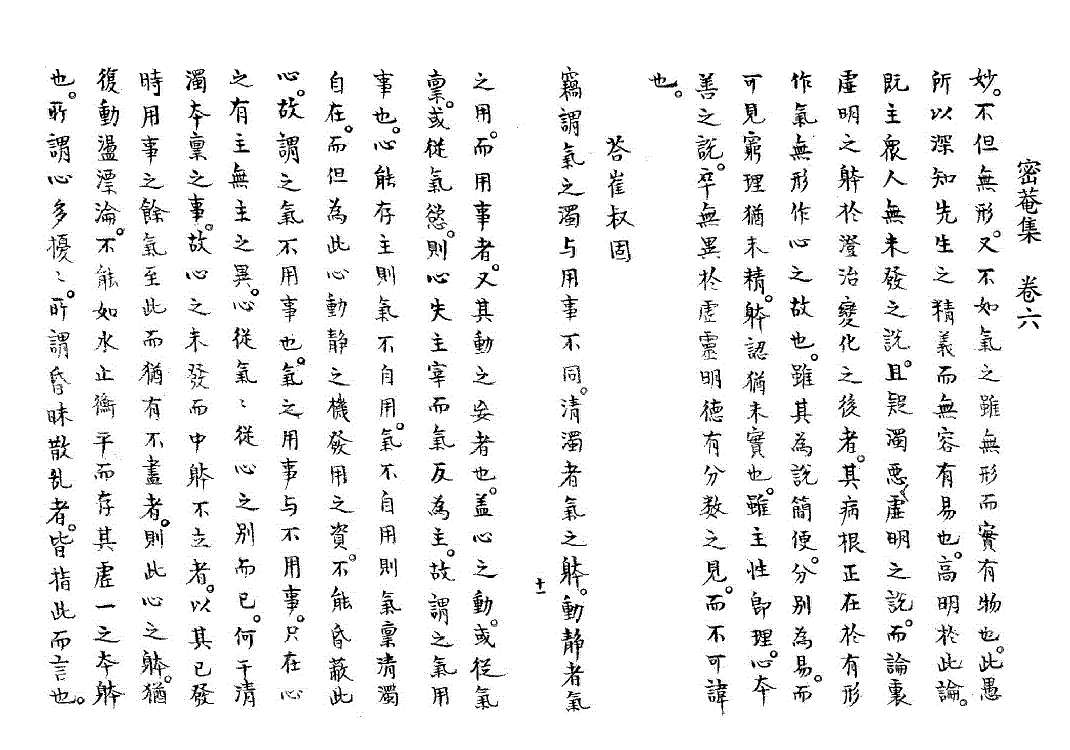 妙。不但无形。又不如气之虽无形而实有物也。此愚所以深知先生之精义而无容有易也。高明于此论。既主众人无未发之说。且疑浊恶里虚明之说。而论虚明之体于澄治变化之后者。其病根正在于有形作气无形作心之故也。虽其为说简便。分别为易。而可见穷理犹未精。体认犹未实也。虽主性即理。心本善之说。卒无异于虚灵明德有分数之见。而不可讳也。
妙。不但无形。又不如气之虽无形而实有物也。此愚所以深知先生之精义而无容有易也。高明于此论。既主众人无未发之说。且疑浊恶里虚明之说。而论虚明之体于澄治变化之后者。其病根正在于有形作气无形作心之故也。虽其为说简便。分别为易。而可见穷理犹未精。体认犹未实也。虽主性即理。心本善之说。卒无异于虚灵明德有分数之见。而不可讳也。答崔叔固
窃谓气之浊与用事不同。清浊者气之体。动静者气之用。而用事者。又其动之妄者也。盖心之动。或从气禀。或从气欲。则心失主宰而气反为主。故谓之气用事也。心能存主则气不自用。气不自用则气禀清浊自在。而但为此心动静之机发用之资。不能昏蔽此心。故谓之气不用事也。气之用事与不用事。只在心之有主无主之异。心从气气从心之别而已。何干清浊本禀之事。故心之未发而中体不立者。以其已发时用事之馀气至此而犹有不尽者。则此心之体。犹复动荡漂沦。不能如水止衡平而存其虚一之本体也。所谓心多扰扰。所谓昏昧散乱者。皆指此而言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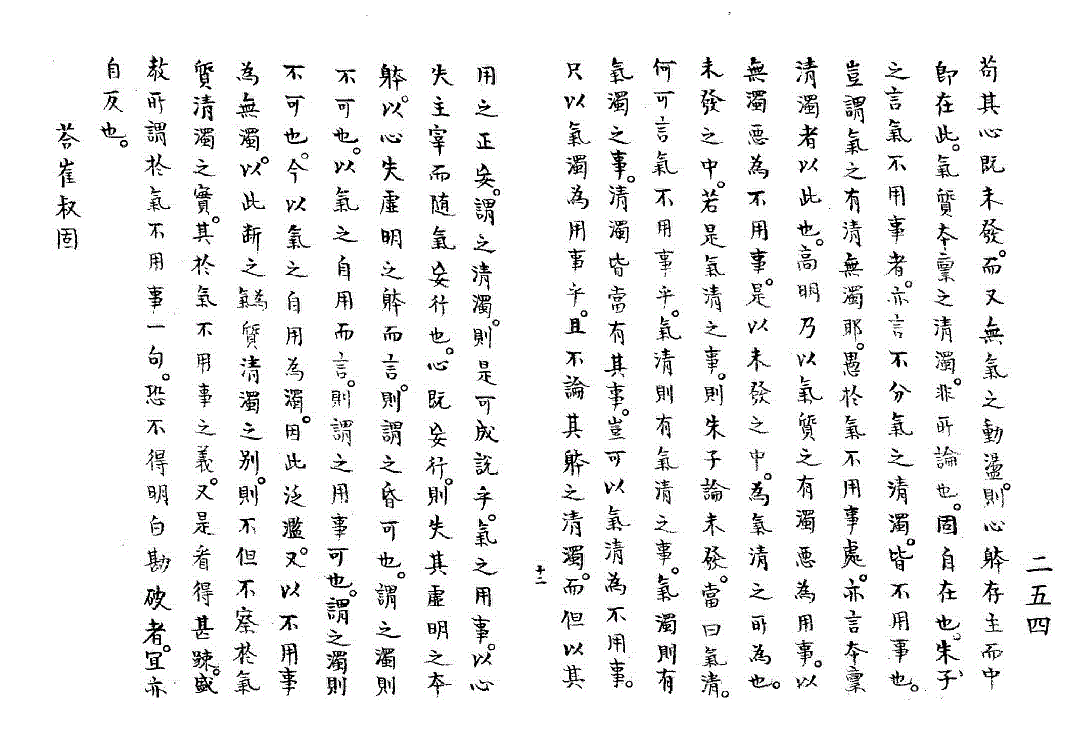 苟其心既未发。而又无气之动荡。则心体存主而中即在此。气质本禀之清浊。非所论也。固自在也。朱子之言气不用事者。亦言不分气之清浊。皆不用事也。岂谓气之有清无浊耶。愚于气不用事处。亦言本禀清浊者以此也。高明乃以气质之有浊恶为用事。以无浊恶为不用事。是以未发之中。为气清之所为也。未发之中。若是气清之事。则朱子论未发。当曰气清。何可言气不用事乎。气清则有气清之事。气浊则有气浊之事。清浊皆当有其事。岂可以气清为不用事。只以气浊为用事乎。且不论其体之清浊。而但以其用之正妄。谓之清浊。则是可成说乎。气之用事。以心失主宰而随气妄行也。心既妄行。则失其虚明之本体。以心失虚明之体而言。则谓之昏可也。谓之浊则不可也。以气之自用而言。则谓之用事可也。谓之浊则不可也。今以气之自用为浊。因此泛滥。又以不用事为无浊。以此断之为气质清浊之别。则不但不察于气质清浊之实。其于气不用事之义。又是看得甚疏。盛教所谓于气不用事一句。恐不得明白勘破者。宜亦自反也。
苟其心既未发。而又无气之动荡。则心体存主而中即在此。气质本禀之清浊。非所论也。固自在也。朱子之言气不用事者。亦言不分气之清浊。皆不用事也。岂谓气之有清无浊耶。愚于气不用事处。亦言本禀清浊者以此也。高明乃以气质之有浊恶为用事。以无浊恶为不用事。是以未发之中。为气清之所为也。未发之中。若是气清之事。则朱子论未发。当曰气清。何可言气不用事乎。气清则有气清之事。气浊则有气浊之事。清浊皆当有其事。岂可以气清为不用事。只以气浊为用事乎。且不论其体之清浊。而但以其用之正妄。谓之清浊。则是可成说乎。气之用事。以心失主宰而随气妄行也。心既妄行。则失其虚明之本体。以心失虚明之体而言。则谓之昏可也。谓之浊则不可也。以气之自用而言。则谓之用事可也。谓之浊则不可也。今以气之自用为浊。因此泛滥。又以不用事为无浊。以此断之为气质清浊之别。则不但不察于气质清浊之实。其于气不用事之义。又是看得甚疏。盛教所谓于气不用事一句。恐不得明白勘破者。宜亦自反也。答崔叔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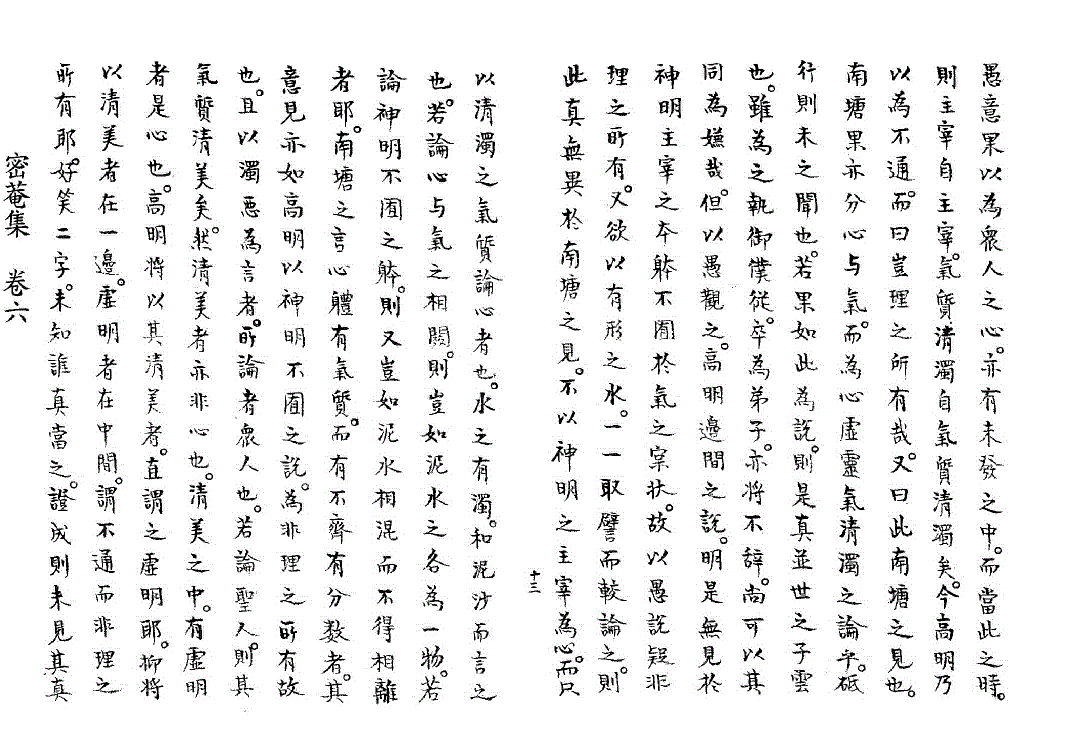 愚意果以为众人之心。亦有未发之中。而当此之时。则主宰自主宰。气质清浊自气质清浊矣。今高明乃以为不通。而曰岂理之所有哉。又曰此南塘之见也。南塘果亦分心与气。而为心虚灵气清浊之论乎。砥行则未之闻也。若果如此为说。则是真并世之子云也。虽为之执御仆从。卒为弟子。亦将不辞。尚可以其同为嫌哉。但以愚观之。高明边间之说。明是无见于神明主宰之本体不囿于气之宲状。故以愚说疑非理之所有。又欲以有形之水。一一取譬而较论之。则此真无异于南塘之见。不以神明之主宰为心。而只以清浊之气质论心者也。水之有浊。和泥沙而言之也。若论心与气之相关。则岂如泥水之各为一物。若论神明不囿之体。则又岂如泥水相混而不得相离者耶。南塘之言心体有气质。而有不齐有分数者。其意见亦如高明以神明不囿之说。为非理之所有故也。且以浊恶为言者。所论者众人也。若论圣人。则其气质清美矣。然清美者亦非心也。清美之中。有虚明者是心也。高明将以其清美者。直谓之虚明耶。抑将以清美者在一边。虚明者在中间。谓不通而非理之所有耶。好笑二字。未知谁真当之。證成则未见其真
愚意果以为众人之心。亦有未发之中。而当此之时。则主宰自主宰。气质清浊自气质清浊矣。今高明乃以为不通。而曰岂理之所有哉。又曰此南塘之见也。南塘果亦分心与气。而为心虚灵气清浊之论乎。砥行则未之闻也。若果如此为说。则是真并世之子云也。虽为之执御仆从。卒为弟子。亦将不辞。尚可以其同为嫌哉。但以愚观之。高明边间之说。明是无见于神明主宰之本体不囿于气之宲状。故以愚说疑非理之所有。又欲以有形之水。一一取譬而较论之。则此真无异于南塘之见。不以神明之主宰为心。而只以清浊之气质论心者也。水之有浊。和泥沙而言之也。若论心与气之相关。则岂如泥水之各为一物。若论神明不囿之体。则又岂如泥水相混而不得相离者耶。南塘之言心体有气质。而有不齐有分数者。其意见亦如高明以神明不囿之说。为非理之所有故也。且以浊恶为言者。所论者众人也。若论圣人。则其气质清美矣。然清美者亦非心也。清美之中。有虚明者是心也。高明将以其清美者。直谓之虚明耶。抑将以清美者在一边。虚明者在中间。谓不通而非理之所有耶。好笑二字。未知谁真当之。證成则未见其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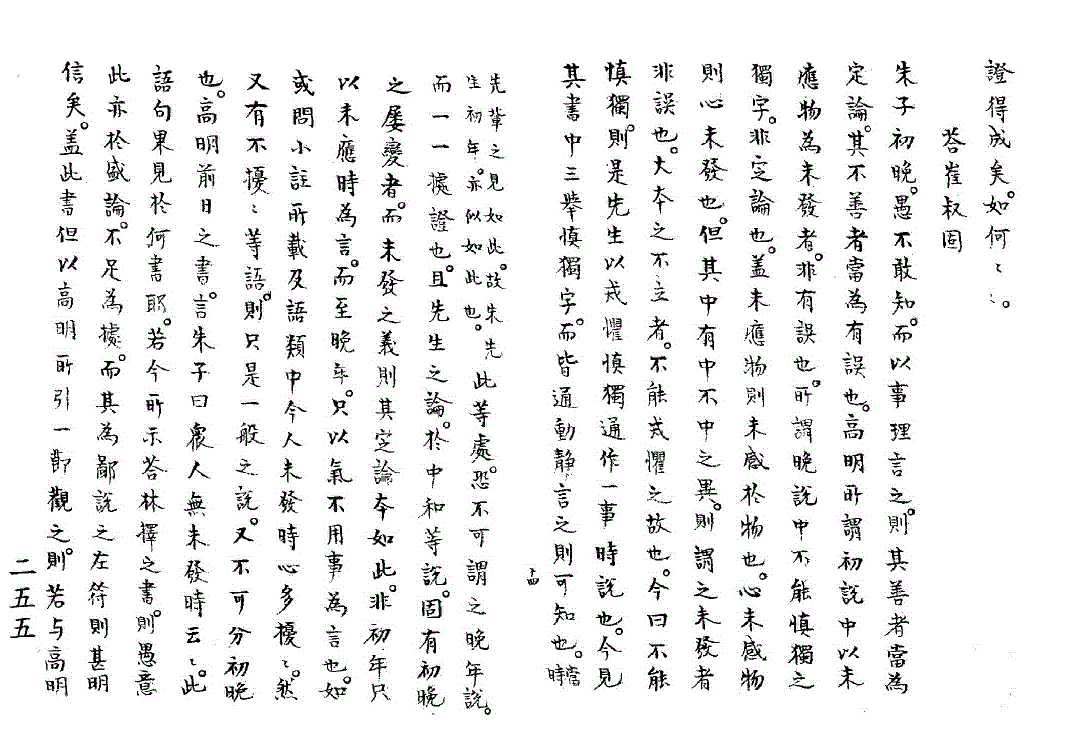 證得成矣。如何如何。
證得成矣。如何如何。答崔叔固
朱子初晚。愚不敢知。而以事理言之。则其善者当为定论。其不善者当为有误也。高明所谓初说中以未应物为未发者。非有误也。所谓晚说中不能慎独之独字。非定论也。盖未应物则未感于物也。心未感物则心未发也。但其中有中不中之异。则谓之未发者非误也。大本之不立者。不能戒惧之故也。今曰不能慎独。则是先生以戒惧慎独通作一事时说也。今见其书中三举慎独字。而皆通动静言之则可知也。(当时先辈之见如此。故朱先生初年。亦似如此也。)此等处。恐不可谓之晚年说。而一一据證也。且先生之论。于中和等说。固有初晚之屡变者。而未发之义则其定论本如此。非初年只以未应时为言。而至晚年。只以气不用事为言也。如或问小注所载及语类中今人未发时心多扰扰。然又有不扰扰等语。则只是一般之说。又不可分初晚也。高明前日之书。言朱子曰众人无未发时云云。此语句果见于何书耶。若今所示答林择之书。则愚意此亦于盛论。不足为据。而其为鄙说之左符则甚明信矣。盖此书但以高明所引一节观之。则若与高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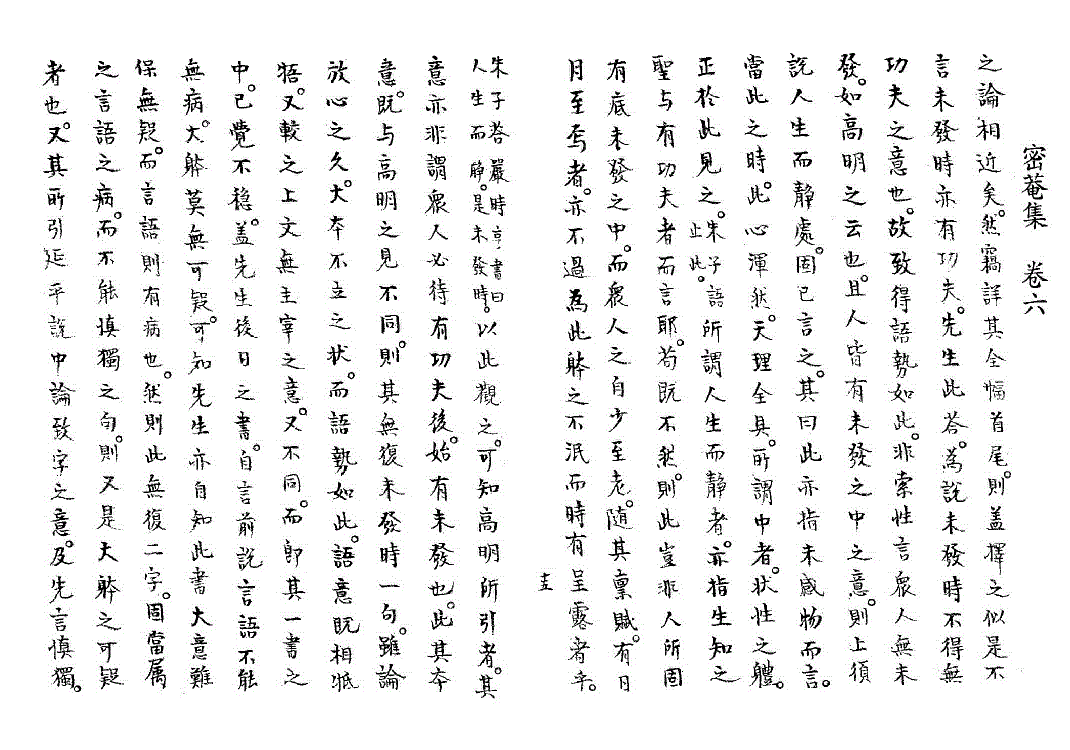 之论相近矣。然窃详其全幅首尾。则盖择之似是不言未发时亦有功夫。先生此答。为说未发时不得无功夫之意也。故致得语势如此。非索性言众人无未发。如高明之云也。且人皆有未发之中之意。则上须说人生而静处。固已言之。其曰此亦指未感物而言。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所谓中者。状性之体。正于此见之。(朱子语止此。)所谓人生而静者。亦指生知之圣与有功夫者而言耶。苟既不然。则此岂非人所固有底未发之中。而众人之自少至老。随其禀赋。有日月至焉者。亦不过为此体之不泯而时有呈露者乎。(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此观之。可知高明所引者。其意亦非谓众人必待有功夫后。始有未发也。此其本意。既与高明之见不同。则其无复未发时一句。虽论放心之久。大本不立之状。而语势如此。语意既相牴牾。又较之上文无主宰之意。又不同。而即其一书之中。已觉不稳。盖先生后日之书。自言前说言语不能无病。大体莫无可疑。可知先生亦自知此书大意难保无疑。而言语则有病也。然则此无复二字。固当属之言语之病。而不能慎独之句。则又是大体之可疑者也。又其所引延乎说中论致字之意。及先言慎独。
之论相近矣。然窃详其全幅首尾。则盖择之似是不言未发时亦有功夫。先生此答。为说未发时不得无功夫之意也。故致得语势如此。非索性言众人无未发。如高明之云也。且人皆有未发之中之意。则上须说人生而静处。固已言之。其曰此亦指未感物而言。当此之时。此心浑然。天理全具。所谓中者。状性之体。正于此见之。(朱子语止此。)所谓人生而静者。亦指生知之圣与有功夫者而言耶。苟既不然。则此岂非人所固有底未发之中。而众人之自少至老。随其禀赋。有日月至焉者。亦不过为此体之不泯而时有呈露者乎。(朱子答严时亨书曰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此观之。可知高明所引者。其意亦非谓众人必待有功夫后。始有未发也。此其本意。既与高明之见不同。则其无复未发时一句。虽论放心之久。大本不立之状。而语势如此。语意既相牴牾。又较之上文无主宰之意。又不同。而即其一书之中。已觉不稳。盖先生后日之书。自言前说言语不能无病。大体莫无可疑。可知先生亦自知此书大意难保无疑。而言语则有病也。然则此无复二字。固当属之言语之病。而不能慎独之句。则又是大体之可疑者也。又其所引延乎说中论致字之意。及先言慎独。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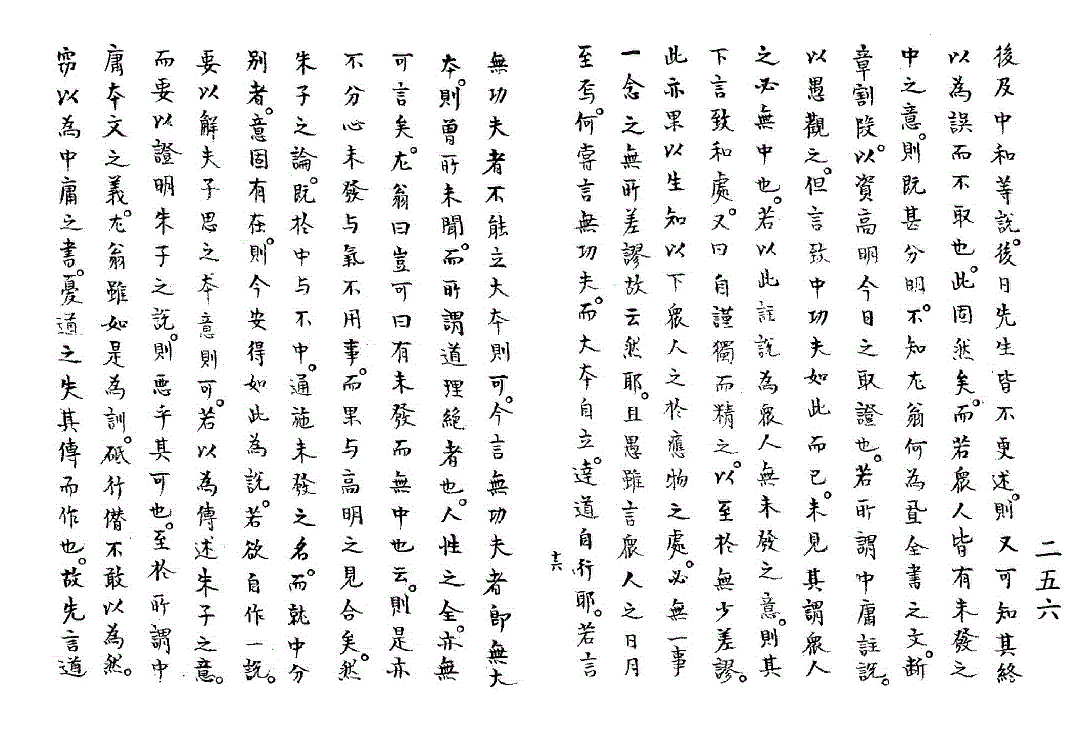 后及中和等说。后日先生皆不更述。则又可知其终以为误而不取也。此固然矣。而若众人皆有未发之中之意。则既甚分明。不知尤翁何为置全书之文。断章割段。以资高明今日之取證也。若所谓中庸注说。以愚观之。但言致中功夫如此而已。未见其谓众人之必无中也。若以此注说为众人无未发之意。则其下言致和处。又曰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无少差谬。此亦果以生知以下众人之于应物之处。必无一事一念之无所差谬故云然耶。且愚虽言众人之日月至焉。何尝言无功夫。而大本自立。达道自行耶。若言无功夫者不能立大本则可。今言无功夫者即无大本。则曾所未闻。而所谓道理绝者也。人性之全。亦无可言矣。尤翁曰岂可曰有未发而无中也云。则是亦不分心未发与气不用事。而果与高明之见合矣。然朱子之论。既于中与不中。通施未发之名。而就中分别者。意固有在。则今安得如此为说。若欲自作一说。要以解夫子思之本意则可。若以为传述朱子之意。而要以證明朱子之说。则恶乎其可也。至于所谓中庸本文之义。尤翁虽如是为训。砥行僭不敢以为然。窃以为中庸之书。忧道之失其传而作也。故先言道
后及中和等说。后日先生皆不更述。则又可知其终以为误而不取也。此固然矣。而若众人皆有未发之中之意。则既甚分明。不知尤翁何为置全书之文。断章割段。以资高明今日之取證也。若所谓中庸注说。以愚观之。但言致中功夫如此而已。未见其谓众人之必无中也。若以此注说为众人无未发之意。则其下言致和处。又曰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无少差谬。此亦果以生知以下众人之于应物之处。必无一事一念之无所差谬故云然耶。且愚虽言众人之日月至焉。何尝言无功夫。而大本自立。达道自行耶。若言无功夫者不能立大本则可。今言无功夫者即无大本。则曾所未闻。而所谓道理绝者也。人性之全。亦无可言矣。尤翁曰岂可曰有未发而无中也云。则是亦不分心未发与气不用事。而果与高明之见合矣。然朱子之论。既于中与不中。通施未发之名。而就中分别者。意固有在。则今安得如此为说。若欲自作一说。要以解夫子思之本意则可。若以为传述朱子之意。而要以證明朱子之说。则恶乎其可也。至于所谓中庸本文之义。尤翁虽如是为训。砥行僭不敢以为然。窃以为中庸之书。忧道之失其传而作也。故先言道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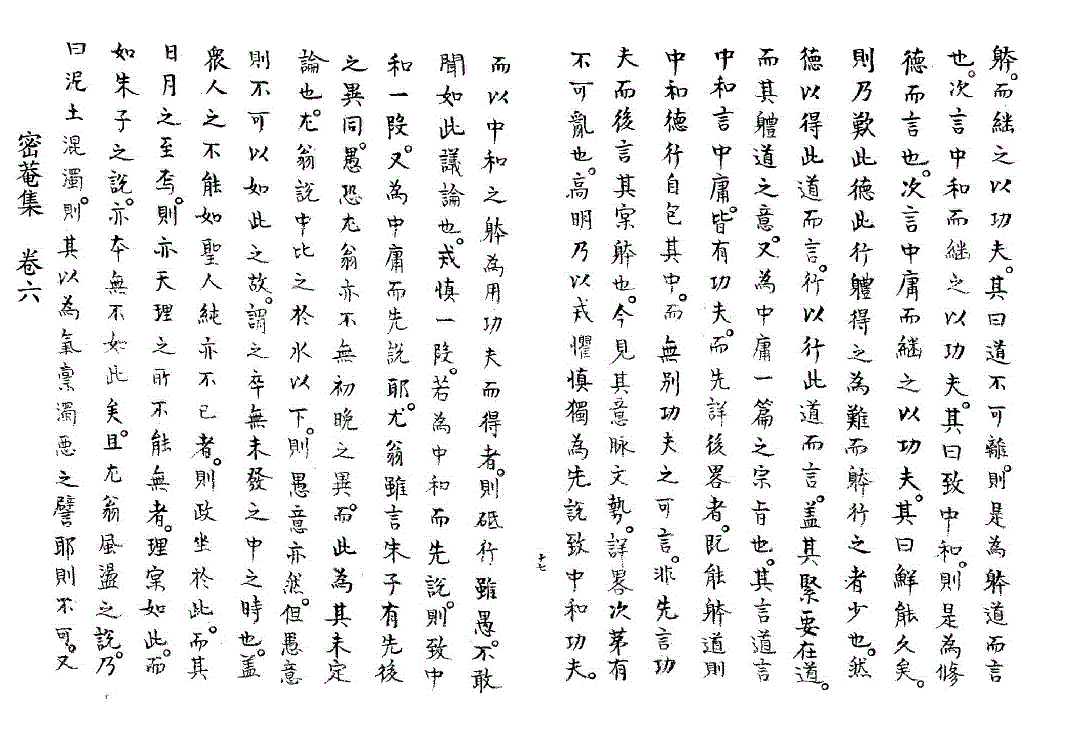 体。而继之以功夫。其曰道不可离。则是为体道而言也。次言中和而继之以功夫。其曰致中和。则是为修德而言也。次言中庸而继之以功夫。其曰鲜能久矣。则乃叹此德此行体得之为难而体行之者少也。然德以得此道而言。行以行此道而言。盖其紧要在道。而其体道之意。又为中庸一篇之宗旨也。其言道言中和言中庸。皆有功夫。而先详后略者。既能体道则中和德行自包其中。而无别功夫之可言。非先言功夫而后言其宲体也。今见其意脉文势。详略次第有不可乱也。高明乃以戒惧慎独为先说致中和功夫。而以中和之体为用功夫而得者。则砥行虽愚。不敢闻如此议论也。戒慎一段。若为中和而先说。则致中和一段。又为中庸而先说耶。尤翁虽言朱子有先后之异同。愚恐尤翁亦不无初晚之异。而此为其未定论也。尤翁说中比之于水以下。则愚意亦然。但愚意则不可以如此之故。谓之卒无未发之中之时也。盖众人之不能如圣人纯亦不已者。则政坐于此。而其日月之至焉。则亦天理之所不能无者。理实如此。而如朱子之说。亦本无不如此矣。且尤翁风荡之说。乃曰泥土混浊。则其以为气禀浊恶之譬耶则不可。又
体。而继之以功夫。其曰道不可离。则是为体道而言也。次言中和而继之以功夫。其曰致中和。则是为修德而言也。次言中庸而继之以功夫。其曰鲜能久矣。则乃叹此德此行体得之为难而体行之者少也。然德以得此道而言。行以行此道而言。盖其紧要在道。而其体道之意。又为中庸一篇之宗旨也。其言道言中和言中庸。皆有功夫。而先详后略者。既能体道则中和德行自包其中。而无别功夫之可言。非先言功夫而后言其宲体也。今见其意脉文势。详略次第有不可乱也。高明乃以戒惧慎独为先说致中和功夫。而以中和之体为用功夫而得者。则砥行虽愚。不敢闻如此议论也。戒慎一段。若为中和而先说。则致中和一段。又为中庸而先说耶。尤翁虽言朱子有先后之异同。愚恐尤翁亦不无初晚之异。而此为其未定论也。尤翁说中比之于水以下。则愚意亦然。但愚意则不可以如此之故。谓之卒无未发之中之时也。盖众人之不能如圣人纯亦不已者。则政坐于此。而其日月之至焉。则亦天理之所不能无者。理实如此。而如朱子之说。亦本无不如此矣。且尤翁风荡之说。乃曰泥土混浊。则其以为气禀浊恶之譬耶则不可。又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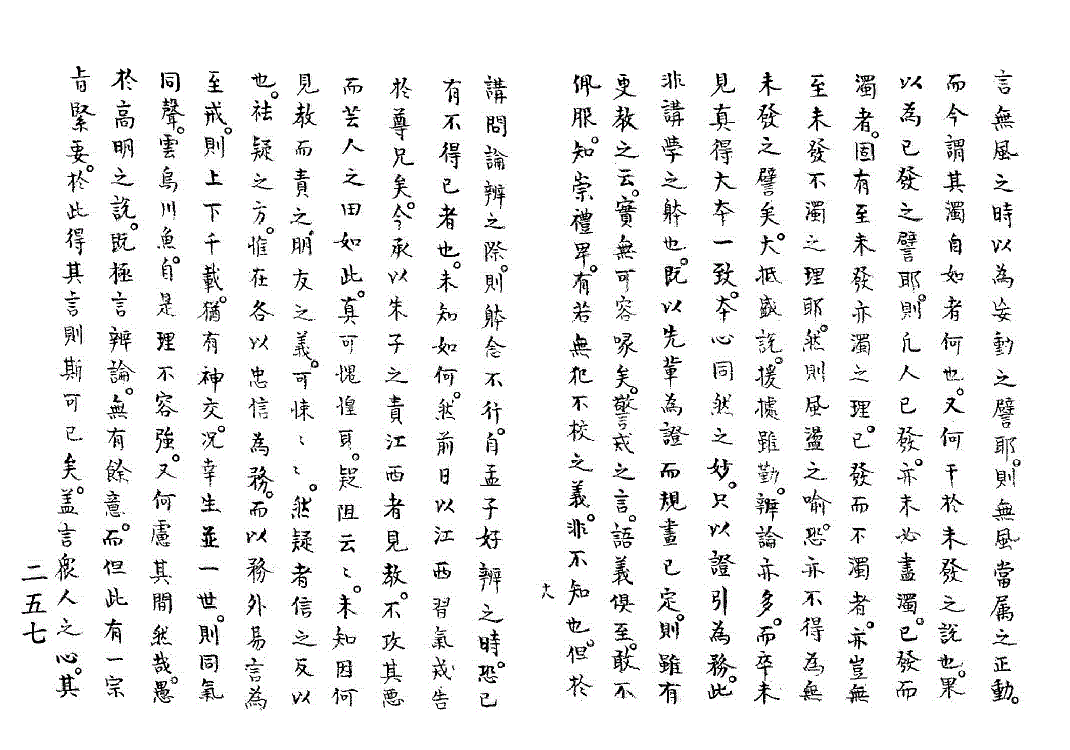 言无风之时以为妄动之譬耶。则无风当属之正动。而今谓其浊自如者何也。又何干于未发之说也。果以为已发之譬耶。则凡人已发。亦未必尽浊。已发而浊者。固有至未发亦浊之理。已发而不浊者。亦岂无至未发不浊之理耶。然则风荡之喻。恐亦不得为无未发之譬矣。大抵盛说。援据虽勤。辨论亦多。而卒未见真得大本一致。本心同然之妙。只以證引为务。此非讲学之体也。既以先辈为證而规画已定。则虽有更教之云。实无可容喙矣。警戒之言。语义俱至。敢不佩服。知崇礼卑。有若无犯不校之义。非不知也。但于讲问论辨之际。则体念不行。自孟子好辨之时。恐已有不得已者也。未知如何。然前日以江西习气戒告于尊兄矣。今承以朱子之责江西者见教。不攻其恶而芸人之田如此。真可愧惶耳。疑阻云云。未知因何见教而责之以朋友之义。可悚可悚。然疑者信之反也。祛疑之方。惟在各以忠信为务。而以务外易言为至戒。则上下千载。犹有神交。况幸生并一世。则同气同声。云乌川鱼。自是理不容强。又何虑其间然哉。愚于高明之说。既极言辨论。无有馀意。而但此有一宗旨紧要。于此得其言则斯可已矣。盖言众人之心。其
言无风之时以为妄动之譬耶。则无风当属之正动。而今谓其浊自如者何也。又何干于未发之说也。果以为已发之譬耶。则凡人已发。亦未必尽浊。已发而浊者。固有至未发亦浊之理。已发而不浊者。亦岂无至未发不浊之理耶。然则风荡之喻。恐亦不得为无未发之譬矣。大抵盛说。援据虽勤。辨论亦多。而卒未见真得大本一致。本心同然之妙。只以證引为务。此非讲学之体也。既以先辈为證而规画已定。则虽有更教之云。实无可容喙矣。警戒之言。语义俱至。敢不佩服。知崇礼卑。有若无犯不校之义。非不知也。但于讲问论辨之际。则体念不行。自孟子好辨之时。恐已有不得已者也。未知如何。然前日以江西习气戒告于尊兄矣。今承以朱子之责江西者见教。不攻其恶而芸人之田如此。真可愧惶耳。疑阻云云。未知因何见教而责之以朋友之义。可悚可悚。然疑者信之反也。祛疑之方。惟在各以忠信为务。而以务外易言为至戒。则上下千载。犹有神交。况幸生并一世。则同气同声。云乌川鱼。自是理不容强。又何虑其间然哉。愚于高明之说。既极言辨论。无有馀意。而但此有一宗旨紧要。于此得其言则斯可已矣。盖言众人之心。其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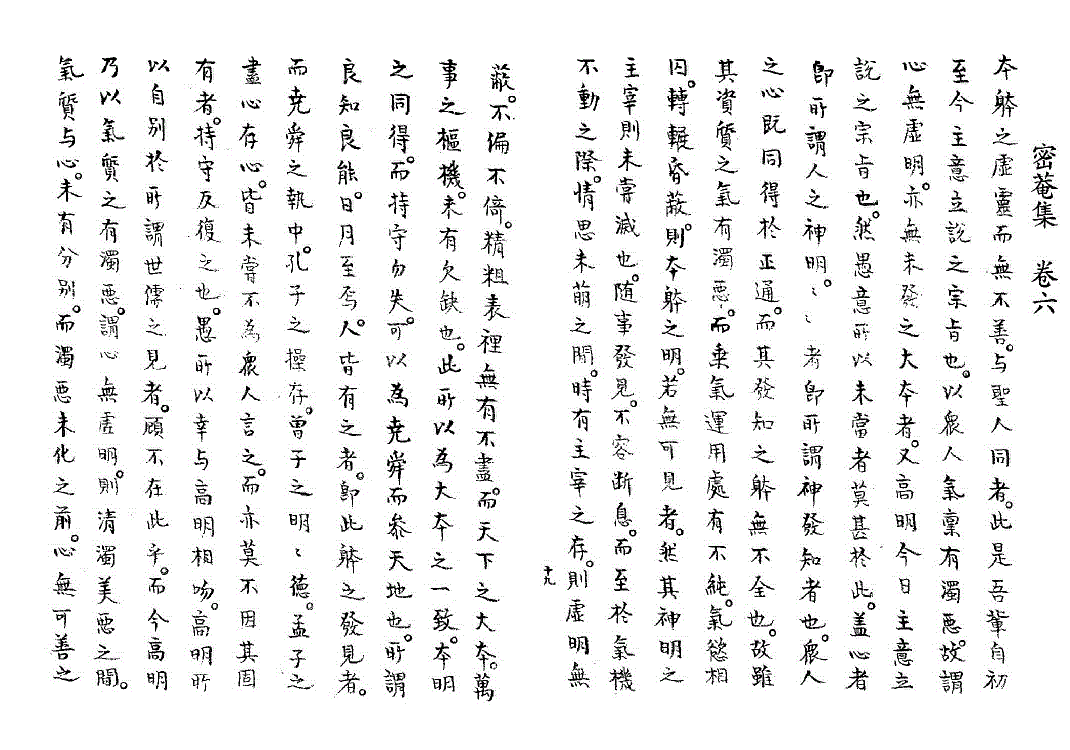 本体之虚灵而无不善。与圣人同者。此是吾辈自初至今主意立说之宗旨也。以众人气禀有浊恶。故谓心无虚明。亦无未发之大本者。又高明今日主意立说之宗旨也。然愚意所以未当者莫甚于此。盖心者即所谓人之神明。神明者即所谓神发知者也。众人之心既同得于正通。而其发知之体无不全也。故虽其资质之气有浊恶。而乘气运用处有不纯。气欲相囚。转辗昏蔽。则本体之明。若无可见者。然其神明之主宰则未尝灭也。随事发见。不容断息。而至于气机不动之际。情思未萌之间。时有主宰之存。则虚明无蔽。不偏不倚。精粗表里无有不尽。而天下之大本。万事之枢机。未有欠缺也。此所以为大本之一致。本明之同得。而持守勿失。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也。所谓良知良能。日月至焉。人皆有之者。即此体之发见者。而尧舜之执中。孔子之操存。曾子之明明德。孟子之尽心存心。皆未尝不为众人言之。而亦莫不因其固有者。持守反复之也。愚所以幸与高明相吻。高明所以自别于所谓世儒之见者。顾不在此乎。而今高明乃以气质之有浊恶。谓心无虚明。则清浊美恶之间。气质与心。未有分别。而浊恶未化之前。心无可善之
本体之虚灵而无不善。与圣人同者。此是吾辈自初至今主意立说之宗旨也。以众人气禀有浊恶。故谓心无虚明。亦无未发之大本者。又高明今日主意立说之宗旨也。然愚意所以未当者莫甚于此。盖心者即所谓人之神明。神明者即所谓神发知者也。众人之心既同得于正通。而其发知之体无不全也。故虽其资质之气有浊恶。而乘气运用处有不纯。气欲相囚。转辗昏蔽。则本体之明。若无可见者。然其神明之主宰则未尝灭也。随事发见。不容断息。而至于气机不动之际。情思未萌之间。时有主宰之存。则虚明无蔽。不偏不倚。精粗表里无有不尽。而天下之大本。万事之枢机。未有欠缺也。此所以为大本之一致。本明之同得。而持守勿失。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也。所谓良知良能。日月至焉。人皆有之者。即此体之发见者。而尧舜之执中。孔子之操存。曾子之明明德。孟子之尽心存心。皆未尝不为众人言之。而亦莫不因其固有者。持守反复之也。愚所以幸与高明相吻。高明所以自别于所谓世儒之见者。顾不在此乎。而今高明乃以气质之有浊恶。谓心无虚明。则清浊美恶之间。气质与心。未有分别。而浊恶未化之前。心无可善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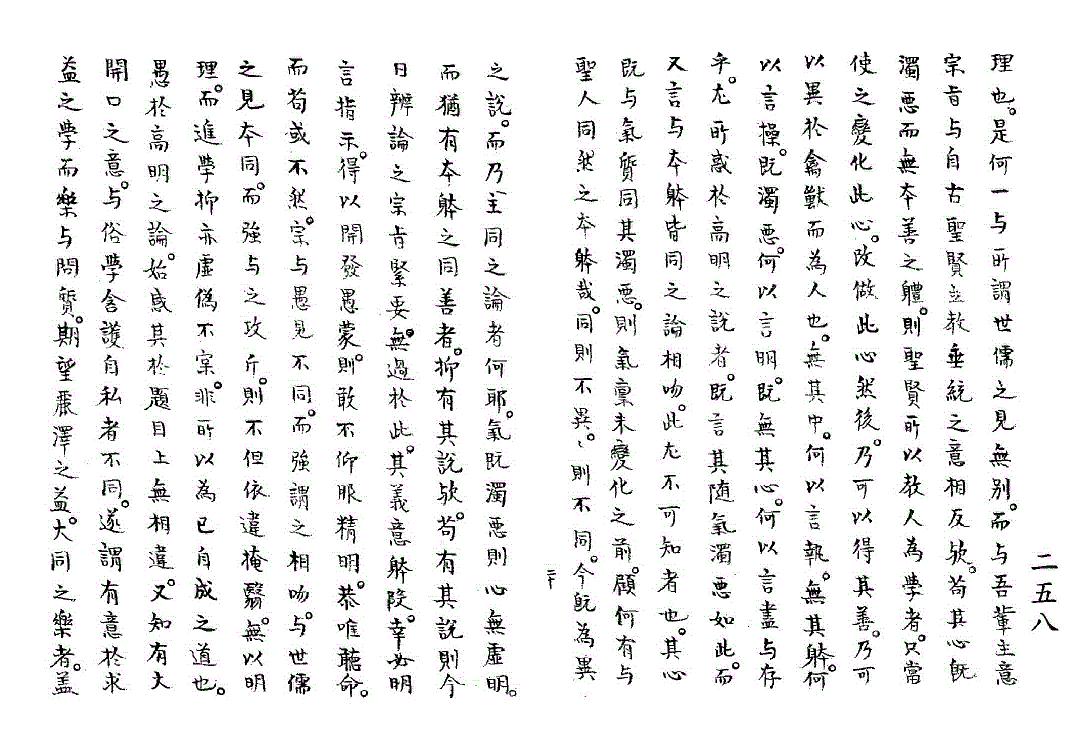 理也。是何一与所谓世儒之见无别。而与吾辈主意宗旨与自古圣贤立教垂统之意相反欤。苟其心既浊恶而无本善之体。则圣贤所以教人为学者。只当使之变化此心。改做此心然后。乃可以得其善。乃可以异于禽兽而为人也。无其中。何以言执。无其体。何以言操。既浊恶。何以言明。既无其心。何以言尽与存乎。尤所惑于高明之说者。既言其随气浊恶如此。而又言与本体皆同之论相吻。此尤不可知者也。其心既与气质同其浊恶。则气禀未变化之前。顾何有与圣人同然之本体哉。同则不异。异则不同。今既为异之说。而乃主同之论者何耶。气既浊恶则心无虚明。而犹有本体之同善者。抑有其说欤。苟有其说则今日辨论之宗旨紧要。无过于此。其义意体段。幸必明言指示。得以开发愚蒙。则敢不仰服精明。恭唯听命。而苟或不然。宗与愚见不同。而强谓之相吻。与世儒之见本同。而强与之攻斤。则不但依违掩翳。无以明理。而进学抑亦虚伪不宲。非所以为己自成之道也。愚于高明之论。始感其于题目上无相违。又知有大开口之意。与俗学含护自私者不同。遂谓有意于求益之学而乐与问质。期望丽泽之益。大同之乐者。盖
理也。是何一与所谓世儒之见无别。而与吾辈主意宗旨与自古圣贤立教垂统之意相反欤。苟其心既浊恶而无本善之体。则圣贤所以教人为学者。只当使之变化此心。改做此心然后。乃可以得其善。乃可以异于禽兽而为人也。无其中。何以言执。无其体。何以言操。既浊恶。何以言明。既无其心。何以言尽与存乎。尤所惑于高明之说者。既言其随气浊恶如此。而又言与本体皆同之论相吻。此尤不可知者也。其心既与气质同其浊恶。则气禀未变化之前。顾何有与圣人同然之本体哉。同则不异。异则不同。今既为异之说。而乃主同之论者何耶。气既浊恶则心无虚明。而犹有本体之同善者。抑有其说欤。苟有其说则今日辨论之宗旨紧要。无过于此。其义意体段。幸必明言指示。得以开发愚蒙。则敢不仰服精明。恭唯听命。而苟或不然。宗与愚见不同。而强谓之相吻。与世儒之见本同。而强与之攻斤。则不但依违掩翳。无以明理。而进学抑亦虚伪不宲。非所以为己自成之道也。愚于高明之论。始感其于题目上无相违。又知有大开口之意。与俗学含护自私者不同。遂谓有意于求益之学而乐与问质。期望丽泽之益。大同之乐者。盖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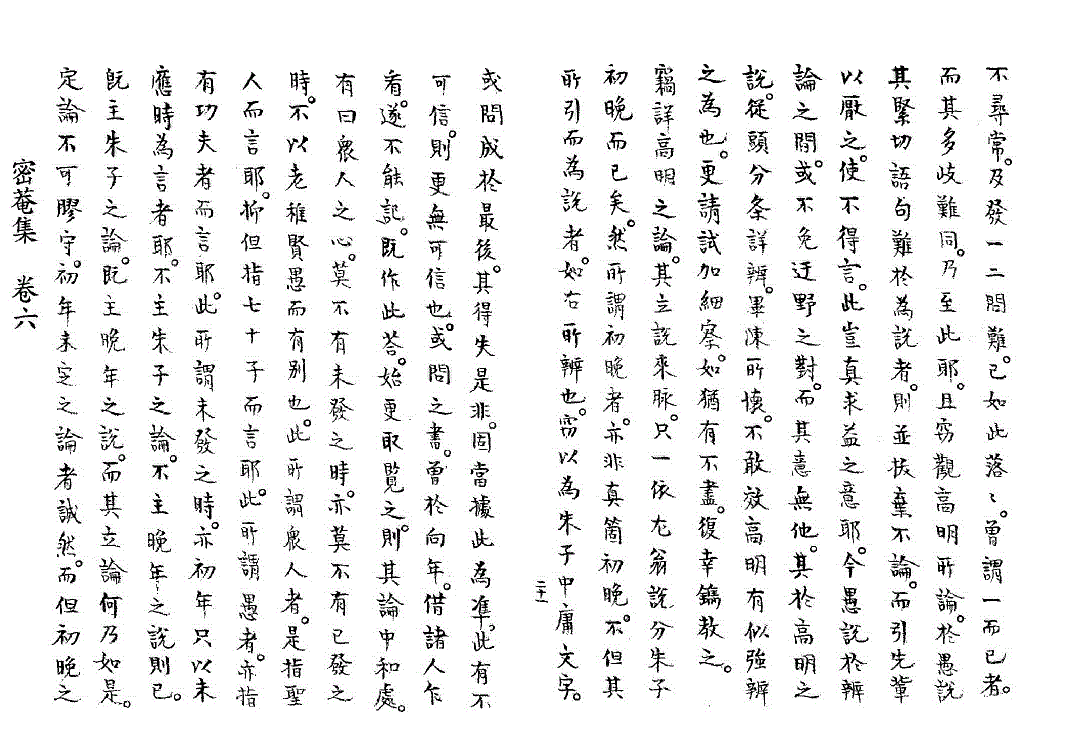 不寻常。及发一二问难。已如此落落。曾谓一而已者。而其多岐难同。乃至此耶。且窃观高明所论。于愚说其紧切语句难于为说者。则并拔弃不论。而引先辈以厌之。使不得言。此岂真求益之意耶。今愚说于辨论之间。或不免迂野之对。而其意无他。其于高明之说。从头分条详辨。毕陈所怀。不敢效高明有似强辨之为也。更请试加细察。如犹有不尽。复幸镌教之。
不寻常。及发一二问难。已如此落落。曾谓一而已者。而其多岐难同。乃至此耶。且窃观高明所论。于愚说其紧切语句难于为说者。则并拔弃不论。而引先辈以厌之。使不得言。此岂真求益之意耶。今愚说于辨论之间。或不免迂野之对。而其意无他。其于高明之说。从头分条详辨。毕陈所怀。不敢效高明有似强辨之为也。更请试加细察。如犹有不尽。复幸镌教之。窃详高明之论。其立说来脉。只一依尤翁说分朱子初晚而已矣。然所谓初晚者。亦非真个初晚。不但其所引而为说者。如右所辨也。窃以为朱子中庸文字。或问成于最后。其得失是非。固当据此为准。此有不可信。则更无可信也。或问之书。曾于向年。借诸人乍看。遂不能记。既作此答。始更取览之。则其论中和处。有曰众人之心。莫不有未发之时。亦莫不有已发之时。不以老稚贤愚而有别也。此所谓众人者。是指圣人而言耶。抑但指七十子而言耶。此所谓愚者。亦指有功夫者而言耶。此所谓未发之时。亦初年只以未应时为言者耶。不主朱子之论。不主晚年之说则已。既主朱子之论。既主晚年之说。而其立论何乃如是。定论不可胶守。初年未定之论者诚然。而但初晚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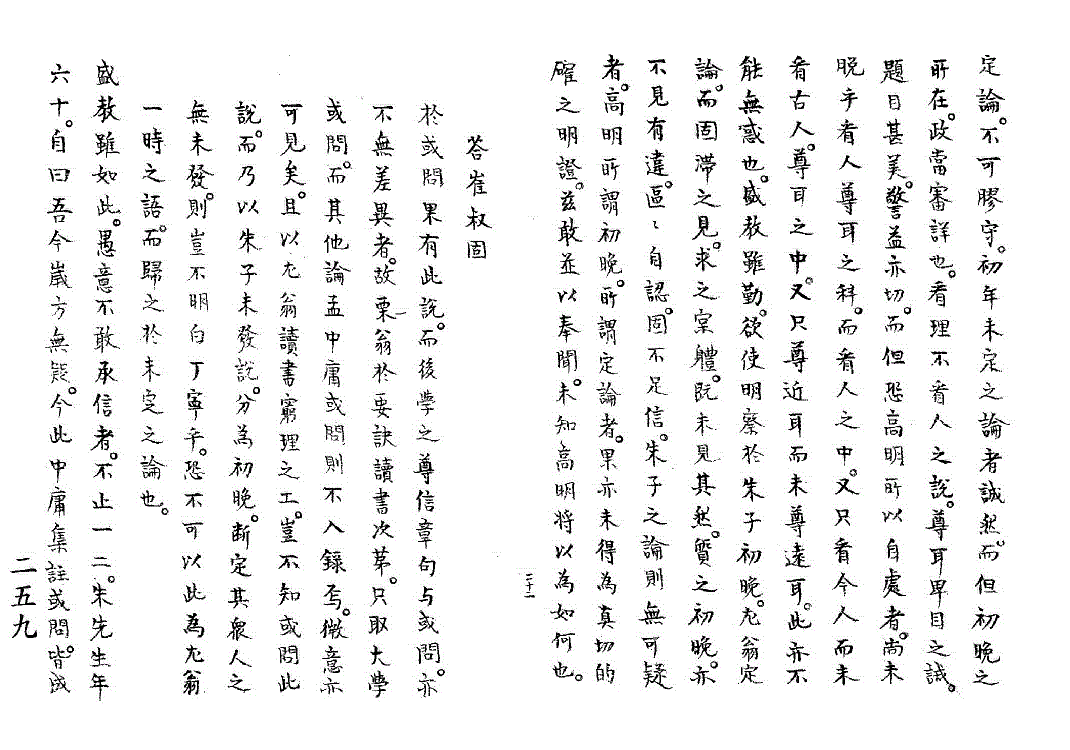 定论。不可胶守。初年未定之论者诚然。而但初晚之所在。政当审详也。看理不看人之说。尊耳卑目之诫。题目甚美。警益亦切。而但恐高明所以自处者。尚未脱乎看人尊耳之科。而看人之中。又只看今人而未看古人。尊耳之中。又只尊近耳而未尊远耳。此亦不能无惑也。盛教虽勤。欲使明察于朱子初晚。尤翁定论。而固滞之见。求之宲体。既未见其然。质之初晚。亦不见有违。区区自认。固不足信。朱子之论则无可疑者。高明所谓初晚。所谓定论者。果亦未得为真切的确之明證。玆敢并以奉闻。未知高明将以为如何也。
定论。不可胶守。初年未定之论者诚然。而但初晚之所在。政当审详也。看理不看人之说。尊耳卑目之诫。题目甚美。警益亦切。而但恐高明所以自处者。尚未脱乎看人尊耳之科。而看人之中。又只看今人而未看古人。尊耳之中。又只尊近耳而未尊远耳。此亦不能无惑也。盛教虽勤。欲使明察于朱子初晚。尤翁定论。而固滞之见。求之宲体。既未见其然。质之初晚。亦不见有违。区区自认。固不足信。朱子之论则无可疑者。高明所谓初晚。所谓定论者。果亦未得为真切的确之明證。玆敢并以奉闻。未知高明将以为如何也。答崔叔固
于或问果有此说。而后学之尊信章句与或问。亦不无差异者。故栗翁于要诀读书次第。只取大学或问。而其他论孟中庸或问则不入录焉。微意亦可见矣。且以尤翁读书穷理之工。岂不知或问此说。而乃以朱子未发说。分为初晚。断定其众人之无未发。则岂不明白丁宁乎。恐不可以此为尤翁一时之语。而归之于未定之论也。
盛教虽如此。愚意不敢承信者。不止一二。朱先生年六十。自曰吾今岁方无疑。今此中庸集注或问。皆成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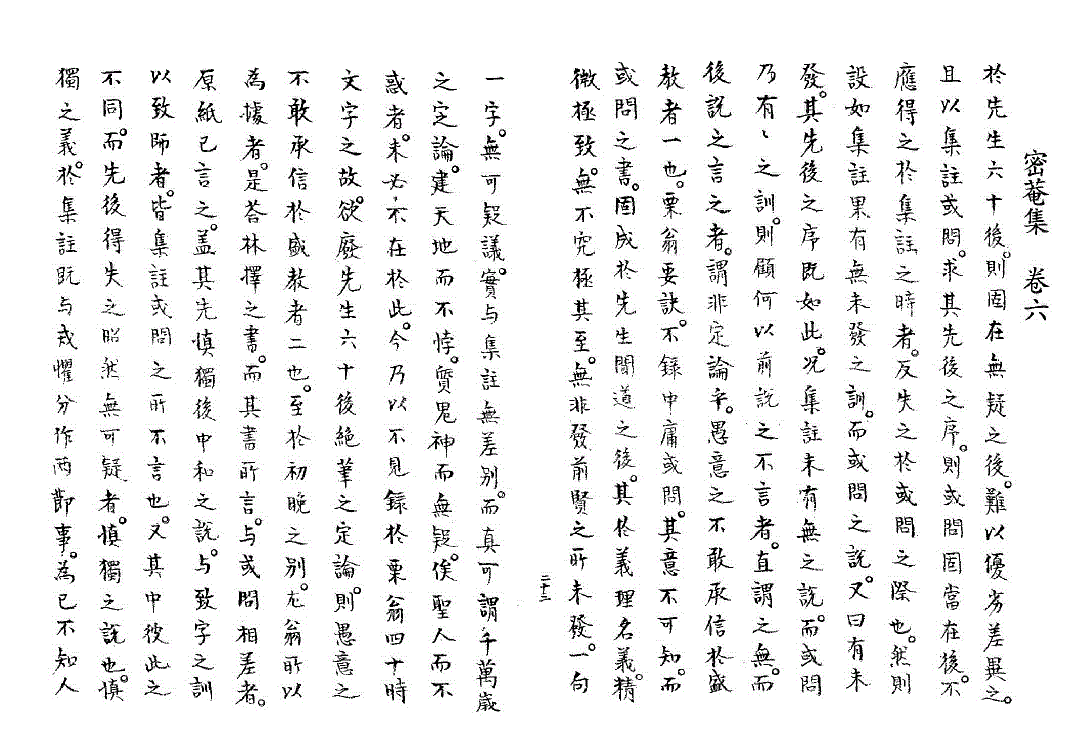 于先生六十后。则固在无疑之后。难以优劣差异之。且以集注或问。求其先后之序。则或问固当在后。不应得之于集注之时者。反失之于或问之际也。然则设如集注果有无未发之训。而或问之说。又曰有未发。其先后之序既如此。况集注未有无之说。而或问乃有有之训。则顾何以前说之不言者。直谓之无。而后说之言之者。谓非定论乎。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一也。栗翁要诀。不录中庸或问。其意不可知。而或问之书。固成于先生闻道之后。其于义理名义。精微极致。无不究极其至。无非发前贤之所未发。一句一字。无可疑议。实与集注无差别。而真可谓千万岁之定论。建天地而不悖。质鬼神而无疑。俟圣人而不惑者。未必不在于此。今乃以不见录于栗翁四十时文字之故。欲废先生六十后绝笔之定论。则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二也。至于初晚之别。尤翁所以为据者。是答林择之书。而其书所言。与或问相差者。原纸已言之。盖其先慎独后中和之说。与致字之训以致师者。皆集注或问之所不言也。又其中彼此之不同。而先后得失之昭然无可疑者。慎独之说也。慎独之义。于集注既与戒惧分作两节事。为己不知人
于先生六十后。则固在无疑之后。难以优劣差异之。且以集注或问。求其先后之序。则或问固当在后。不应得之于集注之时者。反失之于或问之际也。然则设如集注果有无未发之训。而或问之说。又曰有未发。其先后之序既如此。况集注未有无之说。而或问乃有有之训。则顾何以前说之不言者。直谓之无。而后说之言之者。谓非定论乎。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一也。栗翁要诀。不录中庸或问。其意不可知。而或问之书。固成于先生闻道之后。其于义理名义。精微极致。无不究极其至。无非发前贤之所未发。一句一字。无可疑议。实与集注无差别。而真可谓千万岁之定论。建天地而不悖。质鬼神而无疑。俟圣人而不惑者。未必不在于此。今乃以不见录于栗翁四十时文字之故。欲废先生六十后绝笔之定论。则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二也。至于初晚之别。尤翁所以为据者。是答林择之书。而其书所言。与或问相差者。原纸已言之。盖其先慎独后中和之说。与致字之训以致师者。皆集注或问之所不言也。又其中彼此之不同。而先后得失之昭然无可疑者。慎独之说也。慎独之义。于集注既与戒惧分作两节事。为己不知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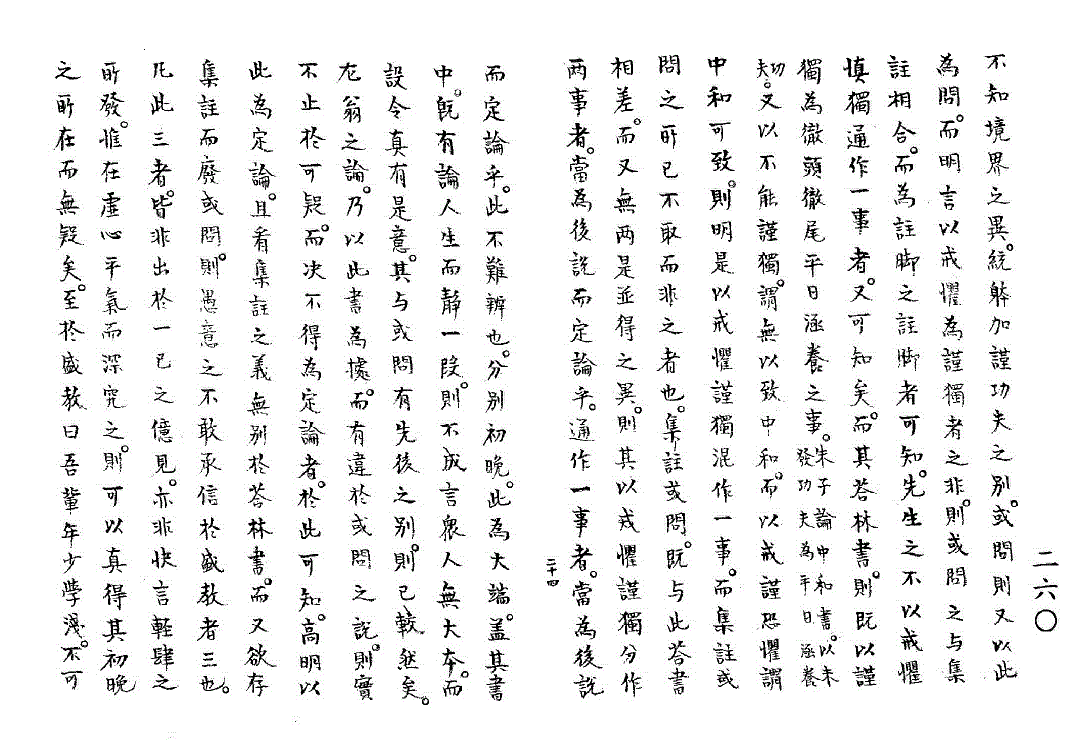 不知境界之异。统体加谨功夫之别。或问则又以此为问。而明言以戒惧为谨独者之非。则或问之与集注相合。而为注脚之注脚者可知。先生之不以戒惧慎独通作一事者。又可知矣。而其答林书。则既以谨独为彻头彻尾平日涵养之事。(朱子论中和书。以未发功夫为平日涵养功夫。)又以不能谨独。谓无以致中和。而以戒谨恐惧谓中和可致。则明是以戒惧谨独混作一事。而集注或问之所已不取而非之者也。集注或问。既与此答书相差。而又无两是并得之异。则其以戒惧谨独分作两事者。当为后说而定论乎。通作一事者。当为后说而定论乎。此不难辨也。分别初晚。此为大端。盖其书中。既有论人生而静一段。则不成言众人无大本。而设令真有是意。其与或问有先后之别。则已较然矣。尤翁之论。乃以此书为据。而有违于或问之说。则实不止于可疑。而决不得为定论者。于此可知。高明以此为定论。且看集注之义无别于答林书。而又欲存集注而废或问。则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三也。凡此三者。皆非出于一己之亿见。亦非快言轻肆之所发。惟在虚心平气而深究之。则可以真得其初晚之所在而无疑矣。至于盛教曰吾辈年少学浅。不可
不知境界之异。统体加谨功夫之别。或问则又以此为问。而明言以戒惧为谨独者之非。则或问之与集注相合。而为注脚之注脚者可知。先生之不以戒惧慎独通作一事者。又可知矣。而其答林书。则既以谨独为彻头彻尾平日涵养之事。(朱子论中和书。以未发功夫为平日涵养功夫。)又以不能谨独。谓无以致中和。而以戒谨恐惧谓中和可致。则明是以戒惧谨独混作一事。而集注或问之所已不取而非之者也。集注或问。既与此答书相差。而又无两是并得之异。则其以戒惧谨独分作两事者。当为后说而定论乎。通作一事者。当为后说而定论乎。此不难辨也。分别初晚。此为大端。盖其书中。既有论人生而静一段。则不成言众人无大本。而设令真有是意。其与或问有先后之别。则已较然矣。尤翁之论。乃以此书为据。而有违于或问之说。则实不止于可疑。而决不得为定论者。于此可知。高明以此为定论。且看集注之义无别于答林书。而又欲存集注而废或问。则愚意之不敢承信于盛教者三也。凡此三者。皆非出于一己之亿见。亦非快言轻肆之所发。惟在虚心平气而深究之。则可以真得其初晚之所在而无疑矣。至于盛教曰吾辈年少学浅。不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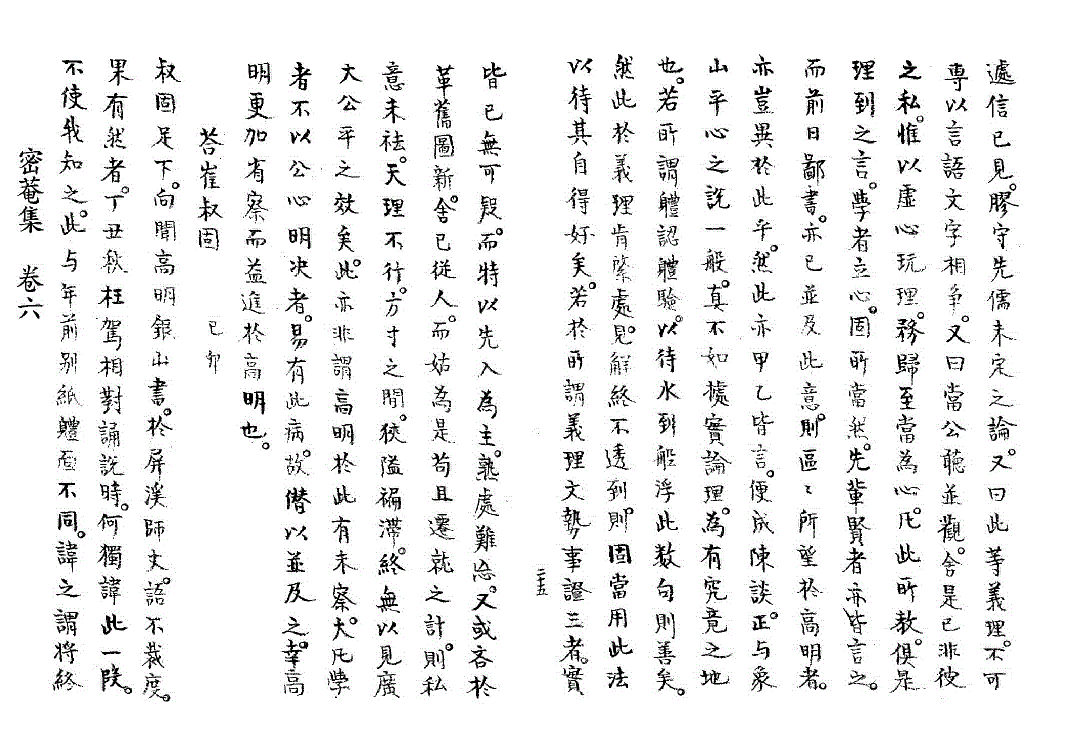 遽信己见。胶守先儒未定之论。又曰此等义理。不可专以言语文字相争。又曰当公听并观。舍是己非彼之私。惟以虚心玩理。务归至当为心。凡此所教。俱是理到之言。学者立心。固所当然。先辈贤者亦皆言之。而前日鄙书。亦已并及此意。则区区所望于高明者。亦岂异于此乎。然此亦甲乙皆言。便成陈谈。正与象山平心之说一般。真不如据实论理。为有究竟之地也。若所谓体认体验。以待水到船浮此数句则善矣。然此于义理肯綮处。见解终不透到。则固当用此法以待其自得好矣。若于所谓义理文势事證三者。实皆已无可疑。而特以先入为主。熟处难忘。又或吝于革旧图新。舍己从人。而姑为是苟且迁就之计。则私意未祛。天理不行。方寸之间。狭隘褊滞。终无以见广大公平之效矣。此亦非谓高明于此有未察。大凡学者不以公心明决者。易有此病。故僭以并及之。幸高明更加省察而益进于高明也。
遽信己见。胶守先儒未定之论。又曰此等义理。不可专以言语文字相争。又曰当公听并观。舍是己非彼之私。惟以虚心玩理。务归至当为心。凡此所教。俱是理到之言。学者立心。固所当然。先辈贤者亦皆言之。而前日鄙书。亦已并及此意。则区区所望于高明者。亦岂异于此乎。然此亦甲乙皆言。便成陈谈。正与象山平心之说一般。真不如据实论理。为有究竟之地也。若所谓体认体验。以待水到船浮此数句则善矣。然此于义理肯綮处。见解终不透到。则固当用此法以待其自得好矣。若于所谓义理文势事證三者。实皆已无可疑。而特以先入为主。熟处难忘。又或吝于革旧图新。舍己从人。而姑为是苟且迁就之计。则私意未祛。天理不行。方寸之间。狭隘褊滞。终无以见广大公平之效矣。此亦非谓高明于此有未察。大凡学者不以公心明决者。易有此病。故僭以并及之。幸高明更加省察而益进于高明也。答崔叔固(己卯)
叔固足下。向闻高明银山书。于屏溪师丈。语不裁度。果有然者。丁丑秋枉驾相对诵说时。何独讳此一段。不使我知之。此与年前别纸体面不同。讳之谓将终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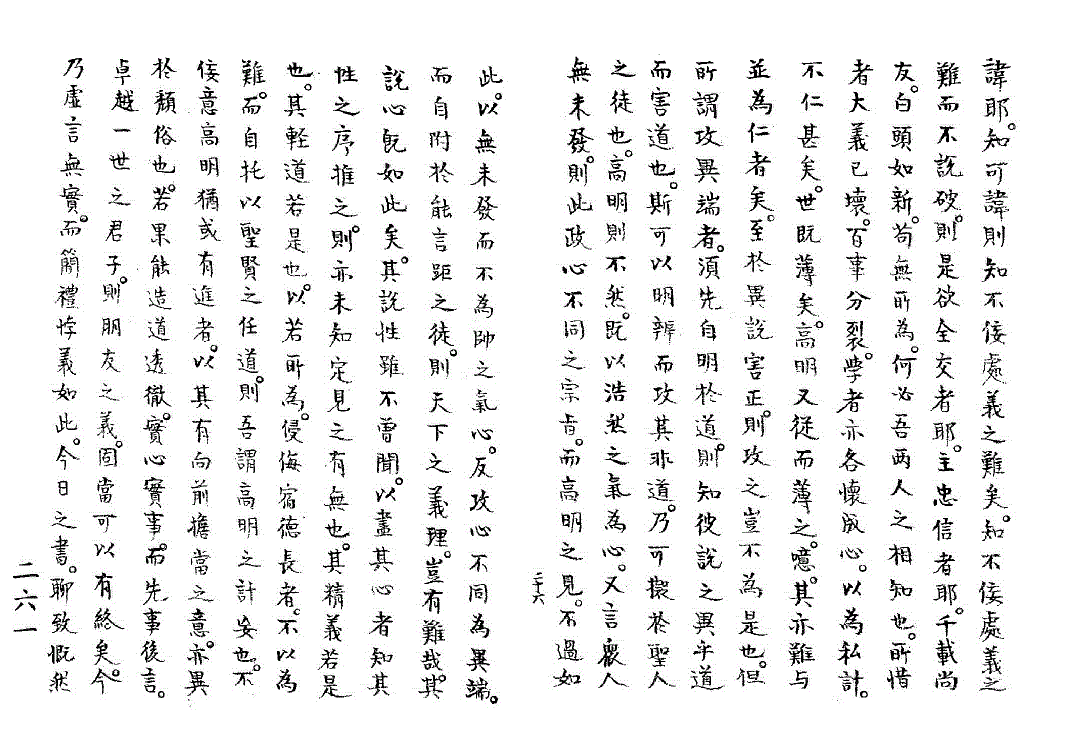 讳耶。知可讳则知不佞处义之难矣。知不佞处义之难而不说破。则是欲全交者耶。主忠信者耶。千载尚友。白头如新。苟无所为。何必吾两人之相知也。所惜者大义已坏。百事分裂。学者亦各怀成心。以为私计。不仁甚矣。世既薄矣。高明又从而薄之。噫。其亦难与并为仁者矣。至于异说害正。则攻之岂不为是也。但所谓攻异端者。须先自明于道。则知彼说之异乎道而害道也。斯可以明辨而攻其非道。乃可拟于圣人之徒也。高明则不然。既以浩然之气为心。又言众人无未发。则此政心不同之宗旨。而高明之见。不过如此。以无未发而不为帅之气心。反攻心不同为异端。而自附于能言距之徒。则天下之义理。岂有难哉。其说心既如此矣。其说性虽不曾闻。以尽其心者知其性之序推之。则亦未知定见之有无也。其精义若是也。其轻道若是也。以若所为。侵侮宿德长者。不以为难。而自托以圣贤之任道。则吾谓高明之计妄也。不佞意高明犹或有进者。以其有句前担当之意。亦异于颓俗也。若果能造道透彻。实心实事。而先事后言。卓越一世之君子。则朋友之义。固当可以有终矣。今乃虚言无实。而简礼悖义如此。今日之书。聊致慨然
讳耶。知可讳则知不佞处义之难矣。知不佞处义之难而不说破。则是欲全交者耶。主忠信者耶。千载尚友。白头如新。苟无所为。何必吾两人之相知也。所惜者大义已坏。百事分裂。学者亦各怀成心。以为私计。不仁甚矣。世既薄矣。高明又从而薄之。噫。其亦难与并为仁者矣。至于异说害正。则攻之岂不为是也。但所谓攻异端者。须先自明于道。则知彼说之异乎道而害道也。斯可以明辨而攻其非道。乃可拟于圣人之徒也。高明则不然。既以浩然之气为心。又言众人无未发。则此政心不同之宗旨。而高明之见。不过如此。以无未发而不为帅之气心。反攻心不同为异端。而自附于能言距之徒。则天下之义理。岂有难哉。其说心既如此矣。其说性虽不曾闻。以尽其心者知其性之序推之。则亦未知定见之有无也。其精义若是也。其轻道若是也。以若所为。侵侮宿德长者。不以为难。而自托以圣贤之任道。则吾谓高明之计妄也。不佞意高明犹或有进者。以其有句前担当之意。亦异于颓俗也。若果能造道透彻。实心实事。而先事后言。卓越一世之君子。则朋友之义。固当可以有终矣。今乃虚言无实。而简礼悖义如此。今日之书。聊致慨然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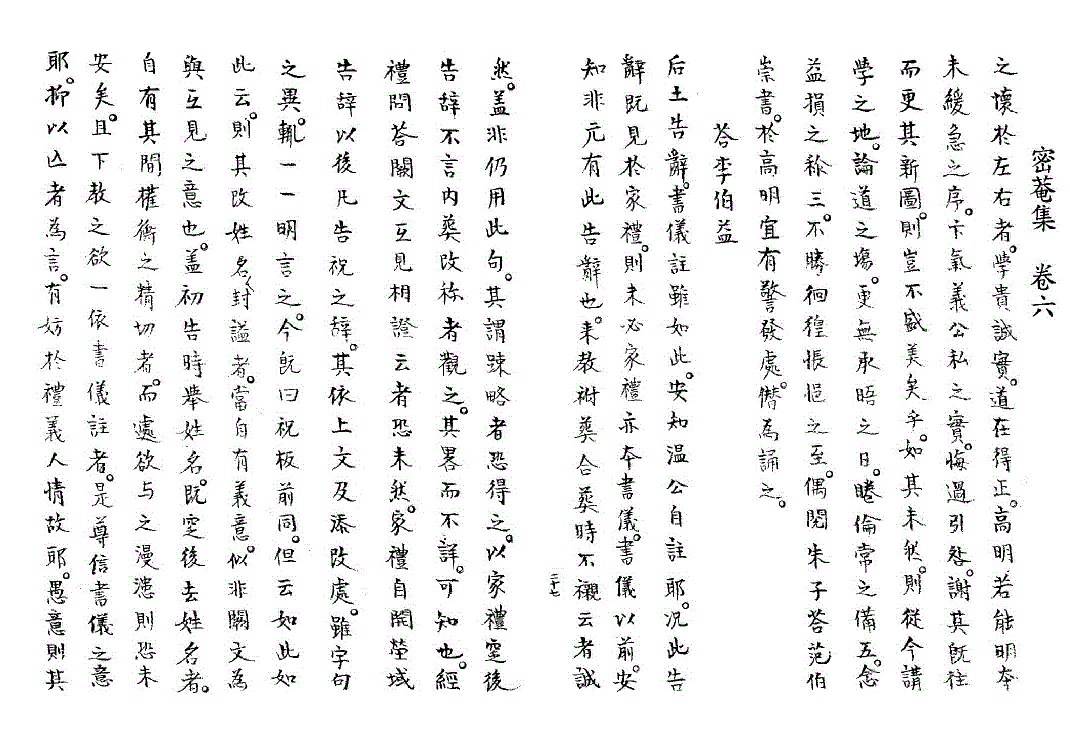 之怀于左右者。学贵诚实。道在得正。高明若能明本末缓急之序。卞气义公私之实。悔过引咎。谢其既往而更其新图。则岂不盛美矣乎。如其未然。则从今讲学之地。论道之场。更无承晤之日。眷伦常之备五。念益损之称三。不胜徊徨怅悒之至。偶阅朱子答范伯崇书。于高明宜有警发处。僭为诵之。
之怀于左右者。学贵诚实。道在得正。高明若能明本末缓急之序。卞气义公私之实。悔过引咎。谢其既往而更其新图。则岂不盛美矣乎。如其未然。则从今讲学之地。论道之场。更无承晤之日。眷伦常之备五。念益损之称三。不胜徊徨怅悒之至。偶阅朱子答范伯崇书。于高明宜有警发处。僭为诵之。答李伯益
后土告辞。书仪注虽如此。安知温公自注耶。况此告辞既见于家礼。则未必家礼亦本书仪。书仪以前。安知非元有此告辞也。来教祔葬合葬时不衬云者诚然。盖非仍用此句。其谓疏略者恐得之。以家礼窆后告辞不言内葬改称者观之。其略而不详。可知也。经礼问答阙文互见相證云者恐未然。家礼自开茔域告辞以后凡告祝之辞。其依上文及添改处。虽字句之异。辄一一明言之。今既曰祝板前同。但云如此如此云。则其改姓名为封谥者。当自有义意。似非阙文与互见之意也。盖初告时举姓名。既窆后去姓名者。自有其间权衡之精切者。而遽欲与之漫漶则恐未安矣。且下教之欲一依书仪注者。是尊信书仪之意耶。抑以亡者为言。有妨于礼义人情故耶。愚意则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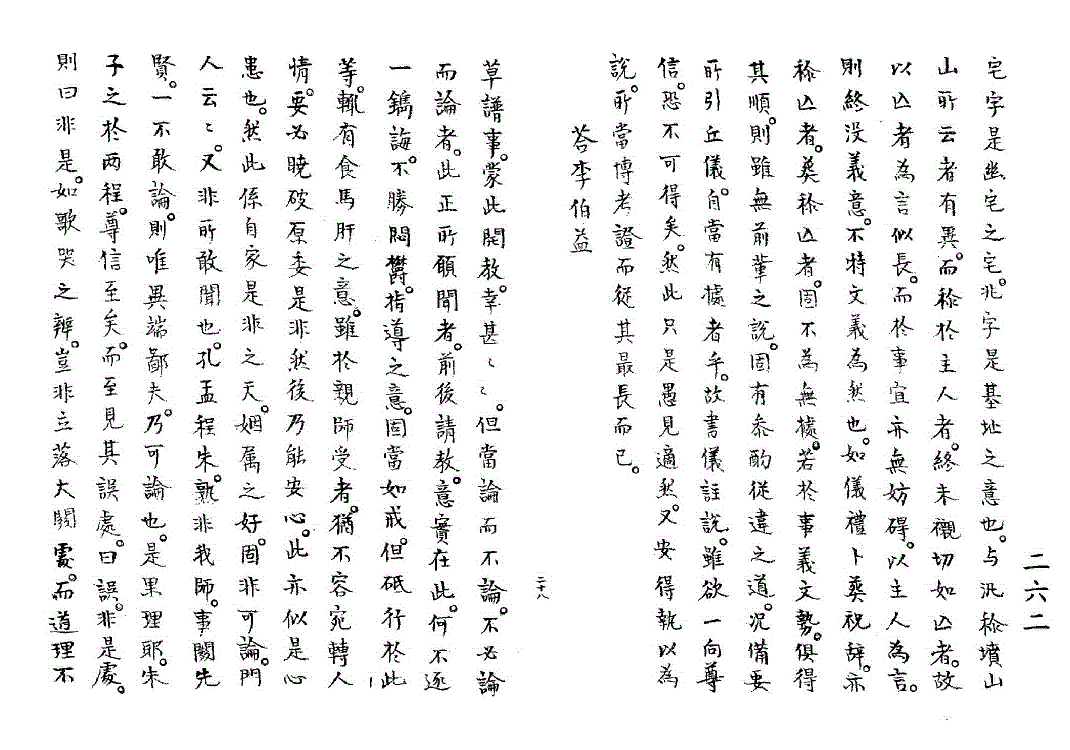 宅字是幽宅之宅。兆字是基址之意也。与汎称坟山山所云者有异。而称于主人者。终未衬切如亡者。故以亡者为言似长。而于事宜亦无妨碍。以主人为言。则终没义意。不特文义为然也。如仪礼卜葬祝辞。亦称亡者。葬称亡者。固不为无据。若于事义文势。俱得其顺。则虽无前辈之说。固有参酌从违之道。况备要所引丘仪。自当有据者乎。故书仪注说。虽欲一向尊信。恐不可得矣。然此只是愚见适然。又安得执以为说。所当博考證而从其最长而已。
宅字是幽宅之宅。兆字是基址之意也。与汎称坟山山所云者有异。而称于主人者。终未衬切如亡者。故以亡者为言似长。而于事宜亦无妨碍。以主人为言。则终没义意。不特文义为然也。如仪礼卜葬祝辞。亦称亡者。葬称亡者。固不为无据。若于事义文势。俱得其顺。则虽无前辈之说。固有参酌从违之道。况备要所引丘仪。自当有据者乎。故书仪注说。虽欲一向尊信。恐不可得矣。然此只是愚见适然。又安得执以为说。所当博考證而从其最长而已。答李伯益
草谱事。蒙此开教。幸甚幸甚。但当论而不论。不必论而论者。此正所愿闻者。前后请教。意实在此。何不逐一镌诲。不胜闷郁。指导之意。固当如戒。但砥行于此等。辄有食马肝之意。虽于亲师受者。犹不容宛转人情。要必晓破原委是非然后乃能安心。此亦似是心患也。然此系自家是非之天。姻属之好。固非可论。门人云云。又非所敢闻也。孔孟程朱。孰非我师。事关先贤。一不敢论。则唯异端鄙夫。乃可论也。是果理耶。朱子之于两程。尊信至矣。而至见其误处。曰误。非是处。则曰非是。如歌哭之辨。岂非立落大关处。而道理不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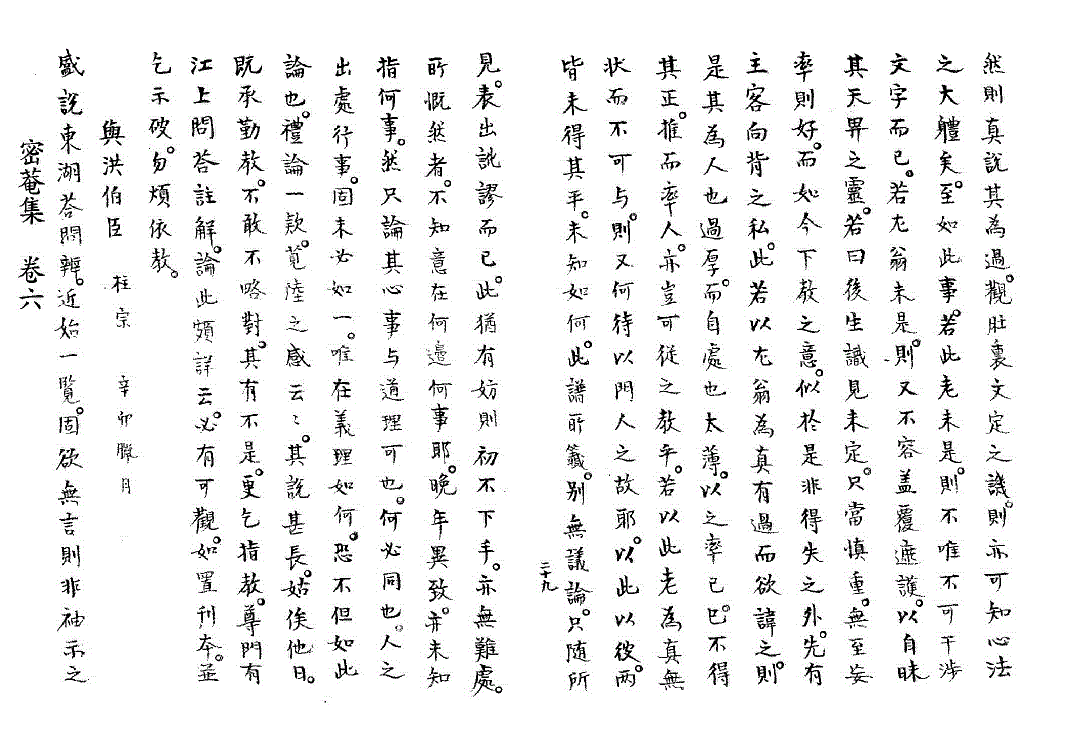 然则真说其为过。观肚里文定之讥。则亦可知心法之大体矣。至如此事。若此老未是。则不唯不可干涉文字而已。若尤翁未是。则又不容盖覆遮护。以自昧其天畀之灵。若曰后生识见未定。只当慎重。无至妄率则好。而如今下教之意。似于是非得失之外。先有主客向背之私。此若以尤翁为真有过而欲讳之。则是其为人也过厚。而自处也太薄。以之率己。己不得其正。推而率人。亦岂可从之教乎。若以此老为真无状而不可与。则又何待以门人之故耶。以此以彼。两皆未得其平。未知如何。此谱所签。别无议论。只随所见。表出讹谬而已。此犹有妨则初不下手。亦无难处。所慨然者。不知意在何边何事耶。晚年异致。亦未知指何事。然只论其心事与道理可也。何必同也。人之出处行事。固未必如一。唯在义理如何。恐不但如此论也。礼论一款。苋陆之感云云。其说甚长。姑俟他日。既承勤教。不敢不略对。其有不是。更乞指教。尊门有江上问答注解。论此颇详云。必有可观。如置刊本。并乞示破。勿烦依教。
然则真说其为过。观肚里文定之讥。则亦可知心法之大体矣。至如此事。若此老未是。则不唯不可干涉文字而已。若尤翁未是。则又不容盖覆遮护。以自昧其天畀之灵。若曰后生识见未定。只当慎重。无至妄率则好。而如今下教之意。似于是非得失之外。先有主客向背之私。此若以尤翁为真有过而欲讳之。则是其为人也过厚。而自处也太薄。以之率己。己不得其正。推而率人。亦岂可从之教乎。若以此老为真无状而不可与。则又何待以门人之故耶。以此以彼。两皆未得其平。未知如何。此谱所签。别无议论。只随所见。表出讹谬而已。此犹有妨则初不下手。亦无难处。所慨然者。不知意在何边何事耶。晚年异致。亦未知指何事。然只论其心事与道理可也。何必同也。人之出处行事。固未必如一。唯在义理如何。恐不但如此论也。礼论一款。苋陆之感云云。其说甚长。姑俟他日。既承勤教。不敢不略对。其有不是。更乞指教。尊门有江上问答注解。论此颇详云。必有可观。如置刊本。并乞示破。勿烦依教。与洪伯臣(柱宗○辛卯腊月)
盛说东湖答问辨。近始一览。固欲无言则非袖示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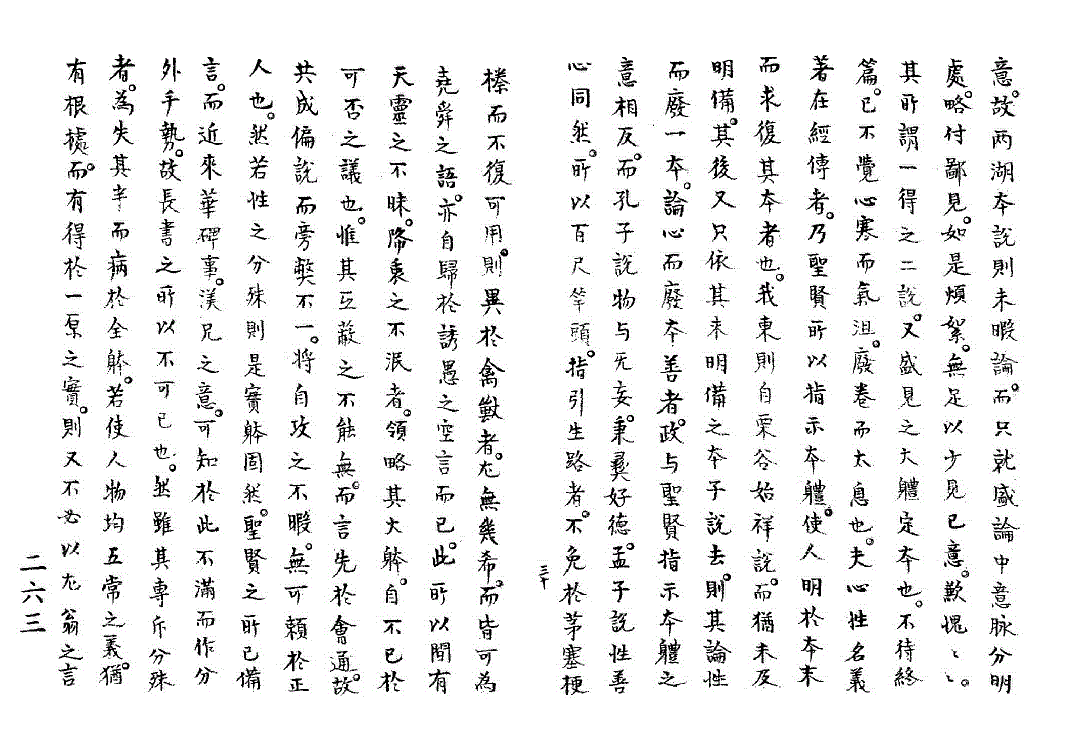 意。故两湖本说则未暇论。而只就盛论中意脉分明处。略付鄙见。如是烦絮。无足以少见己意。歉愧歉愧。其所谓一得之二说。又盛见之大体定本也。不待终篇。已不觉心寒而气沮。废卷而太息也。夫心性名义著在经传者。乃圣贤所以指示本体。使人明于本末而求复其本者也。我东则自栗谷始祥说。而犹未及明备。其后又只依其未明备之本子说去。则其论性而废一本。论心而废本善者。政与圣贤指示本体之意相反。而孔子说物与无妄。秉彝好德。孟子说性善心同然。所以百尺竿头。指引生路者。不免于茅塞梗榛而不复可用。则异于禽兽者。尤无几希。而皆可为尧舜之语。亦自归于诱愚之空言而已。此所以间有天灵之不昧。降衷之不泯者。领略其大体。自不已于可否之议也。惟其互蔽之不能无。而言先于会通。故共成偏说而旁弊不一。将自攻之不暇。无可赖于正人也。然若性之分殊则是实体固然。圣贤之所已备言。而近来华碑事。渼兄之意。可知于此不满而作分外手势。故长书之所以不可已也。然虽其专斥分殊者。为失其半而病于全体。若使人物均五常之义。犹有根据。而有得于一原之实。则又不必以尤翁之言
意。故两湖本说则未暇论。而只就盛论中意脉分明处。略付鄙见。如是烦絮。无足以少见己意。歉愧歉愧。其所谓一得之二说。又盛见之大体定本也。不待终篇。已不觉心寒而气沮。废卷而太息也。夫心性名义著在经传者。乃圣贤所以指示本体。使人明于本末而求复其本者也。我东则自栗谷始祥说。而犹未及明备。其后又只依其未明备之本子说去。则其论性而废一本。论心而废本善者。政与圣贤指示本体之意相反。而孔子说物与无妄。秉彝好德。孟子说性善心同然。所以百尺竿头。指引生路者。不免于茅塞梗榛而不复可用。则异于禽兽者。尤无几希。而皆可为尧舜之语。亦自归于诱愚之空言而已。此所以间有天灵之不昧。降衷之不泯者。领略其大体。自不已于可否之议也。惟其互蔽之不能无。而言先于会通。故共成偏说而旁弊不一。将自攻之不暇。无可赖于正人也。然若性之分殊则是实体固然。圣贤之所已备言。而近来华碑事。渼兄之意。可知于此不满而作分外手势。故长书之所以不可已也。然虽其专斥分殊者。为失其半而病于全体。若使人物均五常之义。犹有根据。而有得于一原之实。则又不必以尤翁之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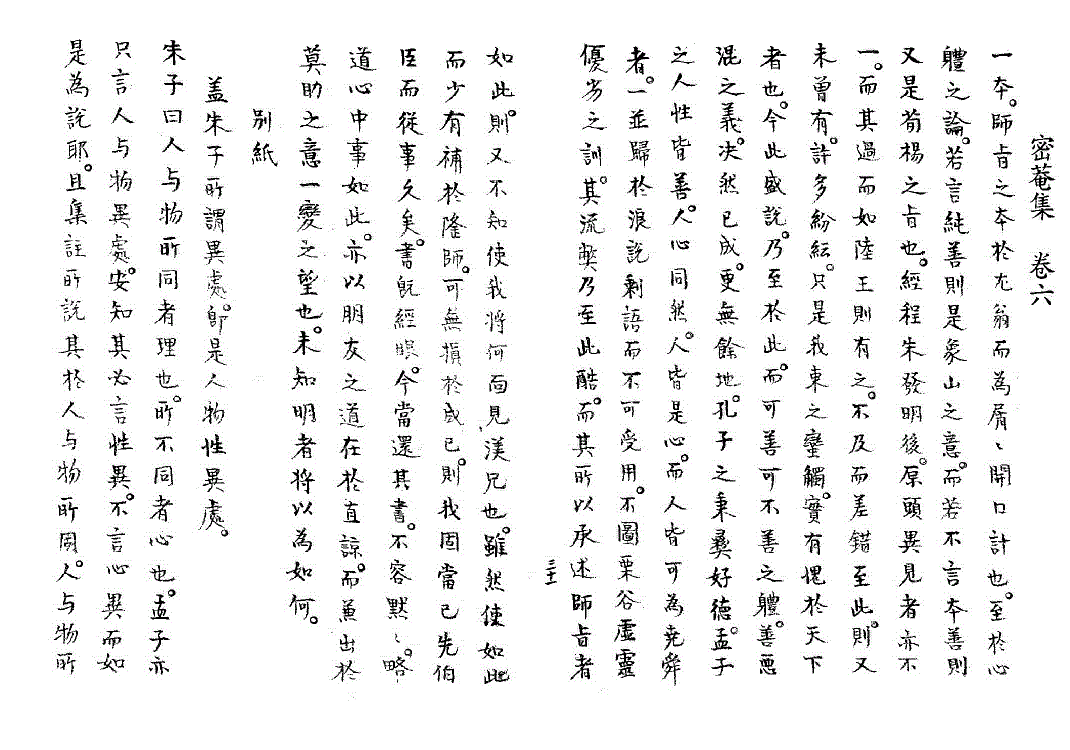 一本。师旨之本于尤翁而为屑屑开口计也。至于心体之论。若言纯善则是象山之意。而若不言本善则又是荀杨之旨也。经程朱发明后。原头异见者亦不一。而其过而如陆王则有之。不及而差错至此。则又未曾有。许多纷纭。只是我东之蛮触。实有愧于天下者也。今此盛说。乃至于此。而可善可不善之体。善恶混之义。决然已成。更无馀地。孔子之秉彝好德。孟子之人性皆善。人心同然。人皆是心。而人皆可为尧舜者。一并归于浪说剩语而不可受用。不图栗谷虚灵优劣之训。其流弊乃至此酷。而其所以承述师旨者如此。则又不知使我将何面见渼兄也。虽然使如此而少有补于隆师。可无损于成己。则我固当已先伯臣而从事久矣。书既经眼。今当还其书。不容默默。略道心中事如此。亦以明友之道在于直谅。而兼出于莫助之意一变之望也。未知明者将以为如何。
一本。师旨之本于尤翁而为屑屑开口计也。至于心体之论。若言纯善则是象山之意。而若不言本善则又是荀杨之旨也。经程朱发明后。原头异见者亦不一。而其过而如陆王则有之。不及而差错至此。则又未曾有。许多纷纭。只是我东之蛮触。实有愧于天下者也。今此盛说。乃至于此。而可善可不善之体。善恶混之义。决然已成。更无馀地。孔子之秉彝好德。孟子之人性皆善。人心同然。人皆是心。而人皆可为尧舜者。一并归于浪说剩语而不可受用。不图栗谷虚灵优劣之训。其流弊乃至此酷。而其所以承述师旨者如此。则又不知使我将何面见渼兄也。虽然使如此而少有补于隆师。可无损于成己。则我固当已先伯臣而从事久矣。书既经眼。今当还其书。不容默默。略道心中事如此。亦以明友之道在于直谅。而兼出于莫助之意一变之望也。未知明者将以为如何。别纸
盖朱子所谓异处。即是人物性异处。
朱子曰人与物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孟子亦只言人与物异处。安知其必言性异。不言心异而如是为说耶。且集注所说其于人与物所同。人与物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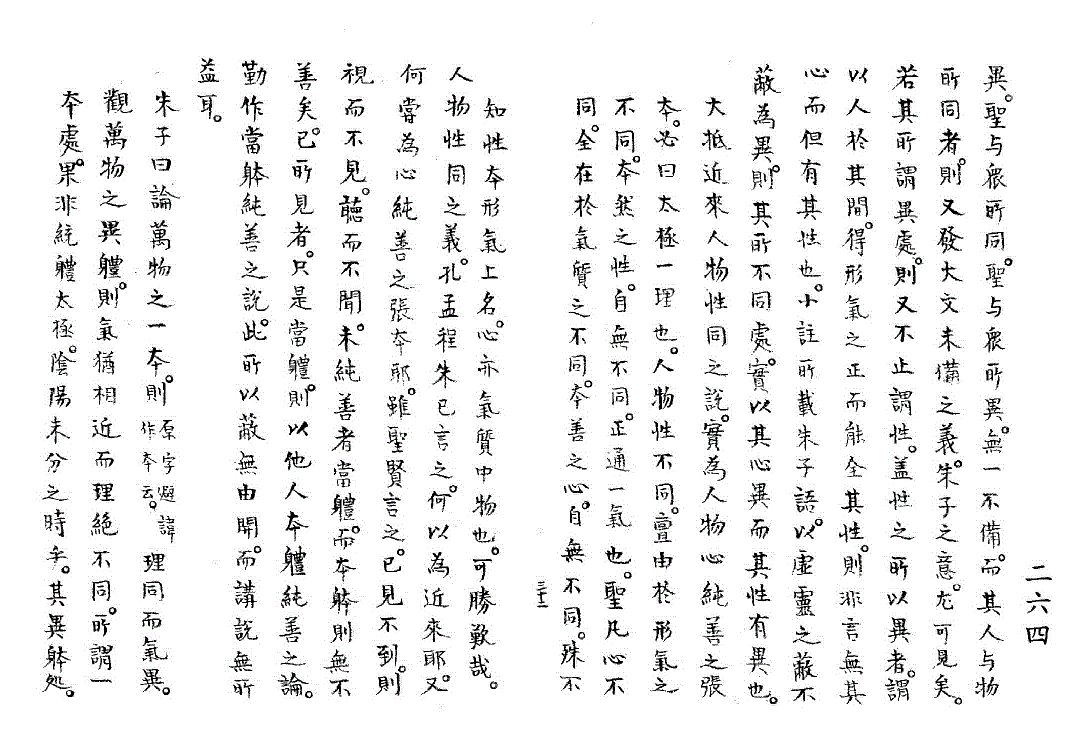 异。圣与众所同。圣与众所异。无一不备。而其人与物所同者。则又发大文未备之义。朱子之意。尤可见矣。若其所谓异处。则又不止谓性。盖性之所以异者。谓以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全其性。则非言无其心而但有其性也。小注所载朱子语。以虚灵之蔽不蔽为异。则其所不同处。实以其心异而其性有异也。
异。圣与众所同。圣与众所异。无一不备。而其人与物所同者。则又发大文未备之义。朱子之意。尤可见矣。若其所谓异处。则又不止谓性。盖性之所以异者。谓以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全其性。则非言无其心而但有其性也。小注所载朱子语。以虚灵之蔽不蔽为异。则其所不同处。实以其心异而其性有异也。大抵近来人物性同之说。实为人物心纯善之张本。必曰太极一理也。人物性不同。亶由于形气之不同。本然之性。自无不同。正通一气也。圣凡心不同。全在于气质之不同。本善之心。自无不同。殊不知性本形气上名。心亦气质中物也。可胜叹哉。
人物性同之义。孔孟程朱已言之。何以为近来耶。又何尝为心纯善之张本耶。虽圣贤言之。己见不到。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未纯善者当体。而本体则无不善矣。己所见者。只是当体。则以他人本体纯善之论。勤作当体纯善之说。此所以蔽无由开。而讲说无所益耳。
朱子曰论万物之一本。则(原字避讳作本云。)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所谓一本处。果非统体太极。阴阳未分之时乎。其异体处。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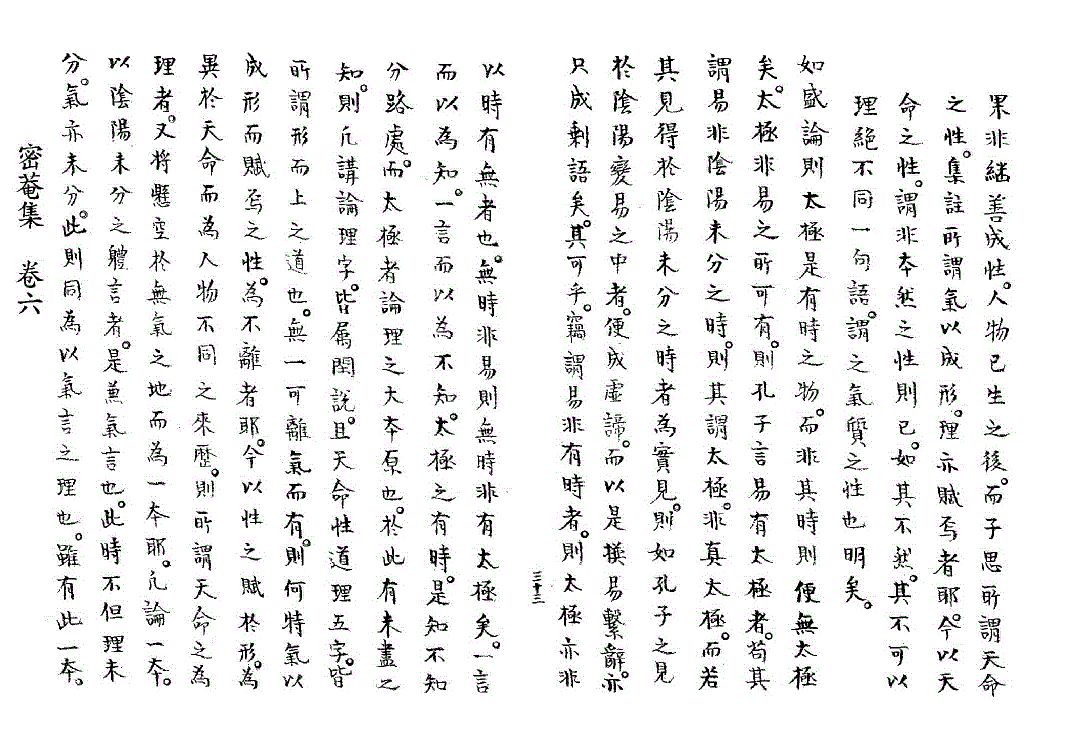 果非继善成性。人物已生之后。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集注所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耶。今以天命之性。谓非本然之性则已。如其不然。其不可以理绝不同一句语。谓之气质之性也明矣。
果非继善成性。人物已生之后。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集注所谓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者耶。今以天命之性。谓非本然之性则已。如其不然。其不可以理绝不同一句语。谓之气质之性也明矣。如盛论则太极是有时之物。而非其时则便无太极矣。太极非易之所可有。则孔子言易有太极者。苟其谓易非阴阳未分之时。则其谓太极。非真太极。而若其见得于阴阳未分之时者为实见。则如孔子之见于阴阳变易之中者。便成虚谛。而以是撰易系辞。亦只成剩语矣。其可乎。窃谓易非有时者。则太极亦非以时有无者也。无时非易则无时非有太极矣。一言而以为知。一言而以为不知。太极之有时。是知不知分路处。而太极者论理之大本原也。于此有未尽之知。则凡讲论理字。皆属闲说。且天命性道理五字。皆所谓形而上之道也。无一可离气而有。则何特气以成形而赋焉之性。为不离者耶。今以性之赋于形。为异于天命而为人物不同之来历。则所谓天命之为理者。又将悬空于无气之地而为一本耶。凡论一本。以阴阳未分之体言者。是兼气言也。此时不但理未分。气亦未分。此则同为以气言之理也。虽有此一本。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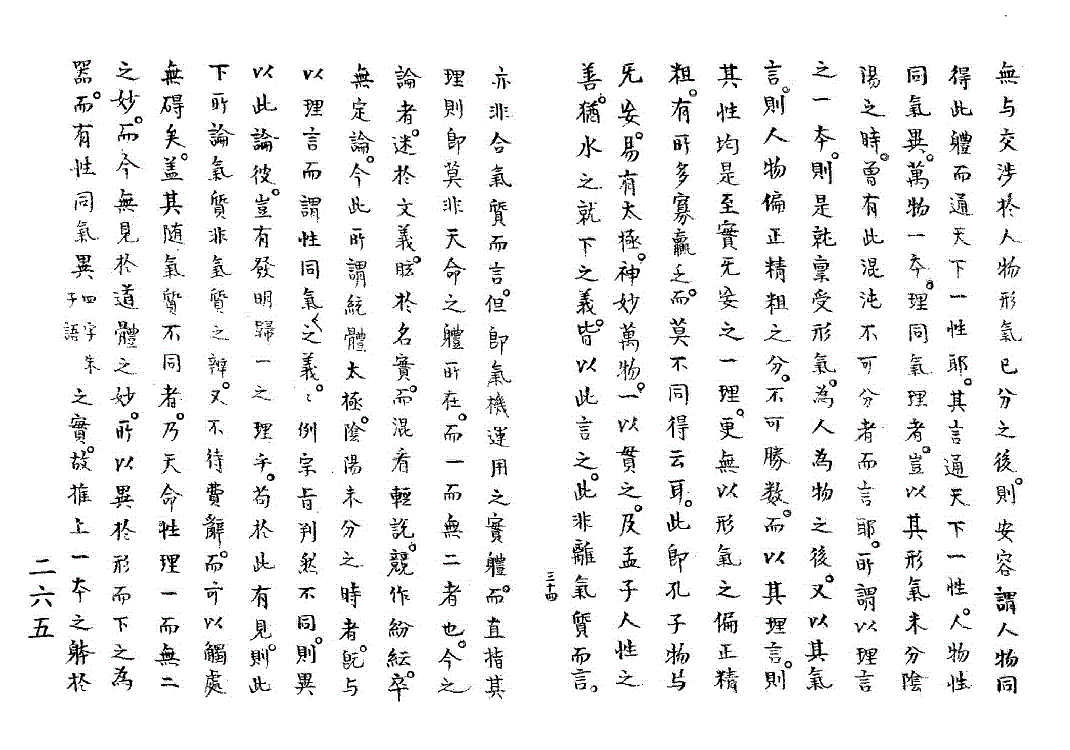 无与交涉于人物形气已分之后。则安容谓人物同得此体而通天下一性耶。其言通天下一性。人物性同气异。万物一本。理同气理者。岂以其形气未分阴阳之时。曾有此混沌不可分者而言耶。所谓以理言之一本。则是就禀受形气。为人为物之后。又以其气言。则人物偏正精粗之分。不可胜数。而以其理言。则其性均是至实无妄之一理。更无以形气之偏正精粗。有所多寡赢乏。而莫不同得云耳。此即孔子物与无妄。易有太极。神妙万物。一以贯之。及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之义。皆以此言之。此非离气质而言。亦非合气质而言。但即气机运用之实体。而直指其理则即莫非天命之体所在。而一而无二者也。今之论者。迷于文义。眩于名实。而混看轻说。竞作纷纭。卒无定论。今此所谓统体太极。阴阳未分之时者。既与以理言而谓性同气异之义。义例宗旨判然不同。则以此论彼。岂有发明归一之理乎。苟于此有见。则此下所论气质非气质之辨。又不待费辞。而可以触处无碍矣。盖其随气质不同者。乃天命性理一而无二之妙。而今无见于道体之妙。所以异于形而下之为器。而有性同气异(四字朱子语)之实。故推上一本之体于
无与交涉于人物形气已分之后。则安容谓人物同得此体而通天下一性耶。其言通天下一性。人物性同气异。万物一本。理同气理者。岂以其形气未分阴阳之时。曾有此混沌不可分者而言耶。所谓以理言之一本。则是就禀受形气。为人为物之后。又以其气言。则人物偏正精粗之分。不可胜数。而以其理言。则其性均是至实无妄之一理。更无以形气之偏正精粗。有所多寡赢乏。而莫不同得云耳。此即孔子物与无妄。易有太极。神妙万物。一以贯之。及孟子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之义。皆以此言之。此非离气质而言。亦非合气质而言。但即气机运用之实体。而直指其理则即莫非天命之体所在。而一而无二者也。今之论者。迷于文义。眩于名实。而混看轻说。竞作纷纭。卒无定论。今此所谓统体太极。阴阳未分之时者。既与以理言而谓性同气异之义。义例宗旨判然不同。则以此论彼。岂有发明归一之理乎。苟于此有见。则此下所论气质非气质之辨。又不待费辞。而可以触处无碍矣。盖其随气质不同者。乃天命性理一而无二之妙。而今无见于道体之妙。所以异于形而下之为器。而有性同气异(四字朱子语)之实。故推上一本之体于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6H 页
 阴阳形气未分之时。而阴阳形气已分之后。则又截然分作。如其形气而有不同。无一本之义也。
阴阳形气未分之时。而阴阳形气已分之后。则又截然分作。如其形气而有不同。无一本之义也。朱子又曰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能(似误)全。此与气犹相近。理绝不同。一般语意。而尤直说露著者也。
天命之性。固是本然之理。性绝不同。则是孟子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者。而朱子既以为气质之性矣。今不先求所以为气质之性之故。而如是硬说可乎。将以朱子之语。为丧心之发乎。抑谓记录之误乎。不然则今日之不思。思而不深。而轻说道体。岂不自归于躁妄。而只为一口之咻豗。无与于宲体者耶。
离形气而有理之名。搭气质而有性之名。理无气质。却无安顿处。而不可谓之性也。
理无气质则无安顿处者。朱子语也。离形气而有理之名。则未曾见之。今此云云。有何据而言耶。既曰无安顿处。则已无无气质而可安顿之理矣。其谓离形气而有理之名者。是又何理而独可离形气可名耶。抑性即理。而理非理而然耶。抑性之理无离气。而理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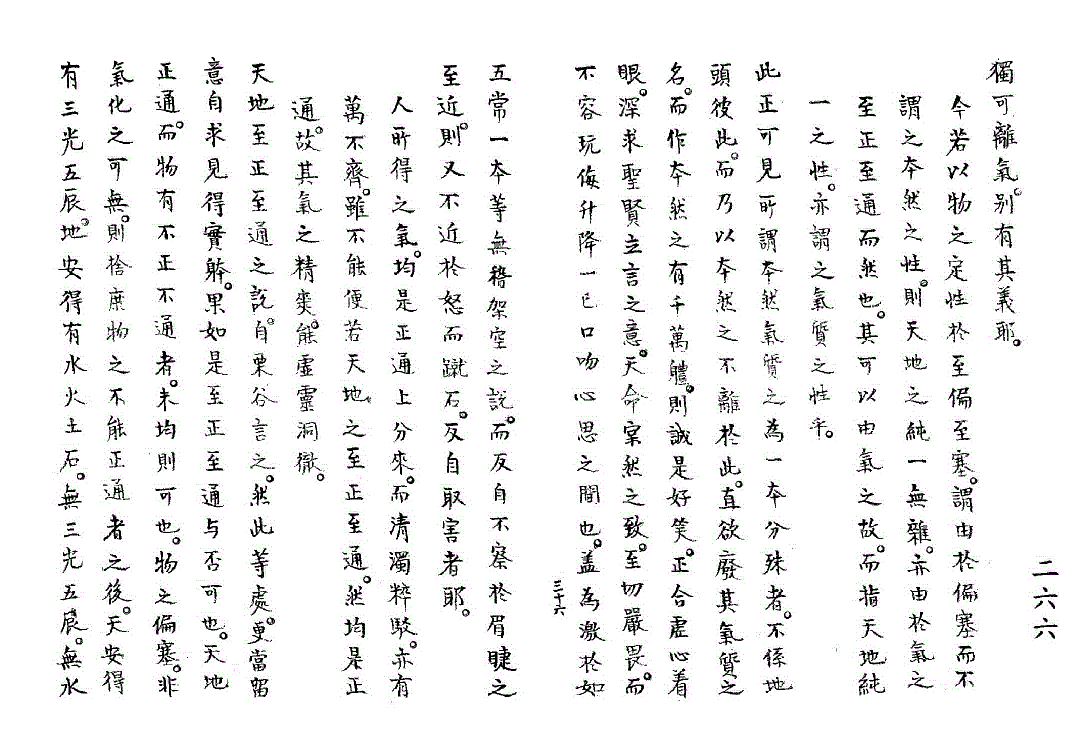 独可离气。别有其义耶。
独可离气。别有其义耶。今若以物之定性于至偏至塞。谓由于偏塞而不谓之本然之性。则天地之纯一无杂。亦由于气之至正至通而然也。其可以由气之故。而指天地纯一之性。亦谓之气质之性乎。
此正可见所谓本然气质之为一本分殊者。不系地头彼此。而乃以本然之不离于此。直欲废其气质之名。而作本然之有千万体。则诚是好笑。正合虚心着眼。深求圣贤立言之意。天命宲然之致。至切严畏。而不容玩侮升降一己口吻心思之间也。盖为激于如五常一本等无稽架空之说。而反自不察于眉睫之至近。则又不近于怒而蹴石。反自取害者耶。
人所得之气。均是正通上分来。而清浊粹驳。亦有万不齐。虽不能便若天地之至正至通。然均是正通。故其气之精爽。能虚灵洞彻。
天地至正至通之说。自栗谷言之。然此等处。更当留意自求见得实体。果如是至正至通与否可也。天地正通。而物有不正不通者。未均则可也。物之偏塞。非气化之可无。则舍庶物之不能正通者之后。天安得有三光五辰。地安得有水火土石。无三光五辰。无水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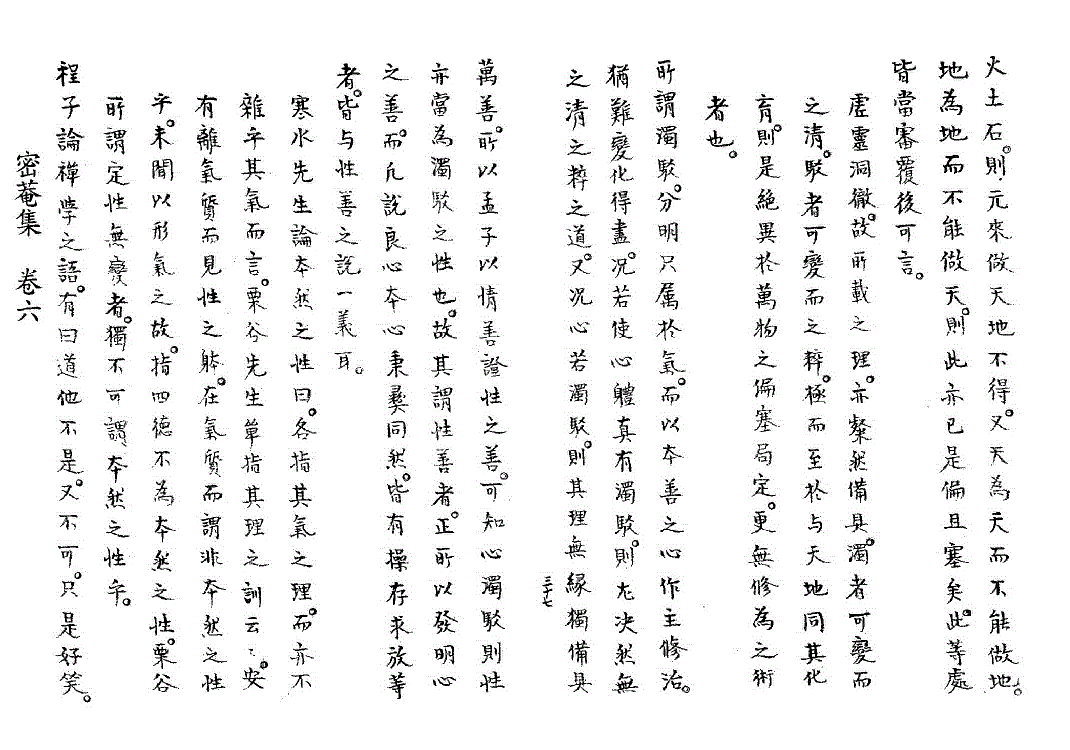 火土石。则元来做天地不得。又天为天而不能做地。地为地而不能做天。则此亦已是偏且塞矣。此等处皆当审覆后可言。
火土石。则元来做天地不得。又天为天而不能做地。地为地而不能做天。则此亦已是偏且塞矣。此等处皆当审覆后可言。虚灵洞彻。故所载之理。亦粲然备具。浊者可变而之清。驳者可变而之粹。极而至于与天地同其化育。则是绝异于万物之偏塞局定。更无修为之术者也。
所谓浊驳。分明只属于气。而以本善之心作主修治。犹难变化得尽。况若使心体真有浊驳。则尤决然无之清之粹之道。又况心若浊驳。则其理无缘独备具万善。所以孟子以情善證性之善。可知心浊驳则性亦当为浊驳之性也。故其谓性善者。正所以发明心之善。而凡说良心本心秉彝同然。皆有操存求放等者。皆与性善之说一义耳。
寒水先生论本然之性曰。各指其气之理。而亦不杂乎其气而言。栗谷先生单指其理之训云云。安有离气质而见性之体。在气质而谓非本然之性乎。未闻以形气之故。指四德不为本然之性。栗谷所谓定性无变者。独不可谓本然之性乎。
程子论禅学之语。有曰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7L 页
 今此所论性字部位皆得。但其不同者。非所谓本然之体。正合留心着精神看。盖人物之性。谓之本然则即是直指性体而言也。性之体一而无二矣。谓之不同。则已是兼指其形气之正通偏塞而言也。不同非性之本体矣。盖性字非不各指其气之理。非离气质而见性之体。又非以在气质而非本然之性也。其言直指性体而为一本所同者。乃直指其气之理不离气质者。则实未尝杂于气质而只是本然之一本耳。但今人不能领会其语意。看出其体段。则非言者误也。正所当自反处也。至如定性云云。则朱子既以为兼心说矣。安得以为本然之性耶。
今此所论性字部位皆得。但其不同者。非所谓本然之体。正合留心着精神看。盖人物之性。谓之本然则即是直指性体而言也。性之体一而无二矣。谓之不同。则已是兼指其形气之正通偏塞而言也。不同非性之本体矣。盖性字非不各指其气之理。非离气质而见性之体。又非以在气质而非本然之性也。其言直指性体而为一本所同者。乃直指其气之理不离气质者。则实未尝杂于气质而只是本然之一本耳。但今人不能领会其语意。看出其体段。则非言者误也。正所当自反处也。至如定性云云。则朱子既以为兼心说矣。安得以为本然之性耶。诚如是者。牛顺马健。牛耕马驰。皆当以气质之性目之。而如有牛而不能顺不能耕。马而不能健不能驰者。将不可谓气质之性。而谓之何惟也哉。
孔子之言人为贵。孟子之言犬牛人不同。此以形质言。周子之言刚柔善恶中。程子之言气清气浊。张子之言形而后有气质之性。此以资质言。此二者皆由气而分。则皆所以谓之气质之性也。朱子之说。于此最详备。何不细考。其言有曰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曰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曰性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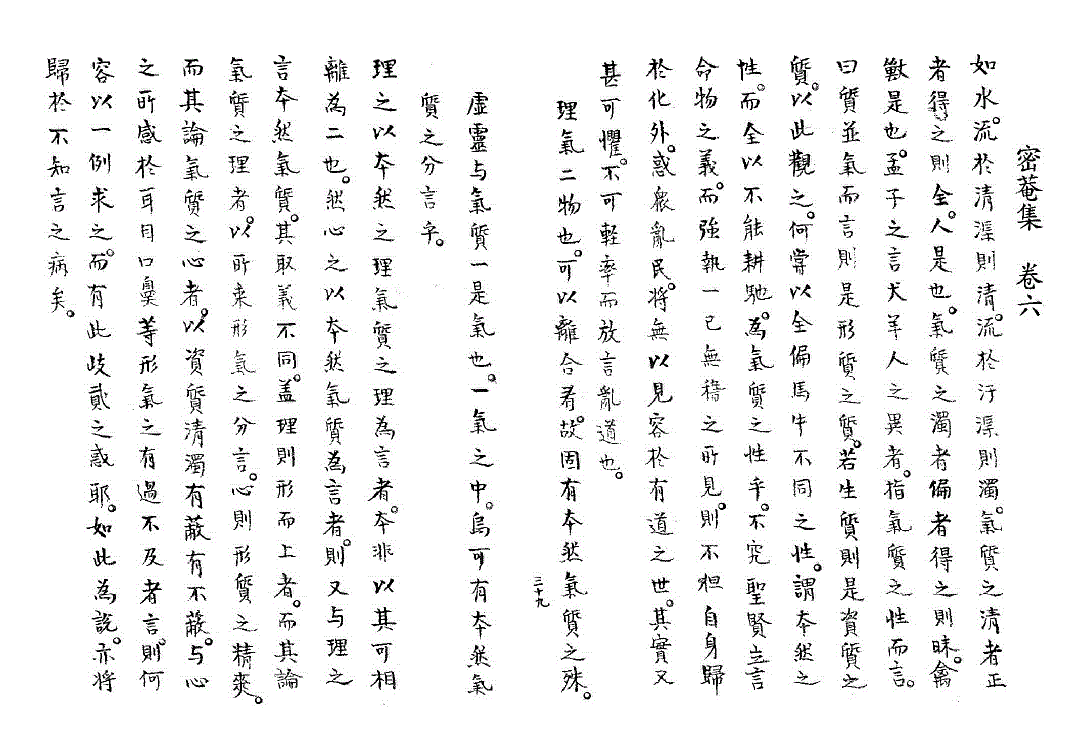 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于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孟子之言犬羊人之异者。指气质之性而言。曰质并气而言则是形质之质。若生质则是资质之质。以此观之。何尝以全偏马牛不同之性。谓本然之性。而全以不能耕驰。为气质之性乎。不究圣贤立言命物之义。而强执一己无稽之所见。则不但自身归于化外。惑众乱民。将无以见容于有道之世。其实又甚可惧。不可轻率而放言乱道也。
如水。流于清渠则清。流于污渠则浊。气质之清者正者得之则全。人是也。气质之浊者偏者得之则昧。禽兽是也。孟子之言犬羊人之异者。指气质之性而言。曰质并气而言则是形质之质。若生质则是资质之质。以此观之。何尝以全偏马牛不同之性。谓本然之性。而全以不能耕驰。为气质之性乎。不究圣贤立言命物之义。而强执一己无稽之所见。则不但自身归于化外。惑众乱民。将无以见容于有道之世。其实又甚可惧。不可轻率而放言乱道也。理气二物也。可以离合看。故固有本然气质之殊。虚灵与气质一是气也。一气之中。乌可有本然气质之分言乎。
理之以本然之理气质之理为言者。本非以其可相离为二也。然心之以本然气质为言者。则又与理之言本然气质。其取义不同。盖理则形而上者。而其论气质之理者。以所乘形气之分言。心则形质之精爽。而其论气质之心者。以资质清浊有蔽有不蔽。与心之所感于耳目口鼻等形气之有过不及者言。则何容以一例求之。而有此歧贰之惑耶。如此为说。亦将归于不知言之病矣。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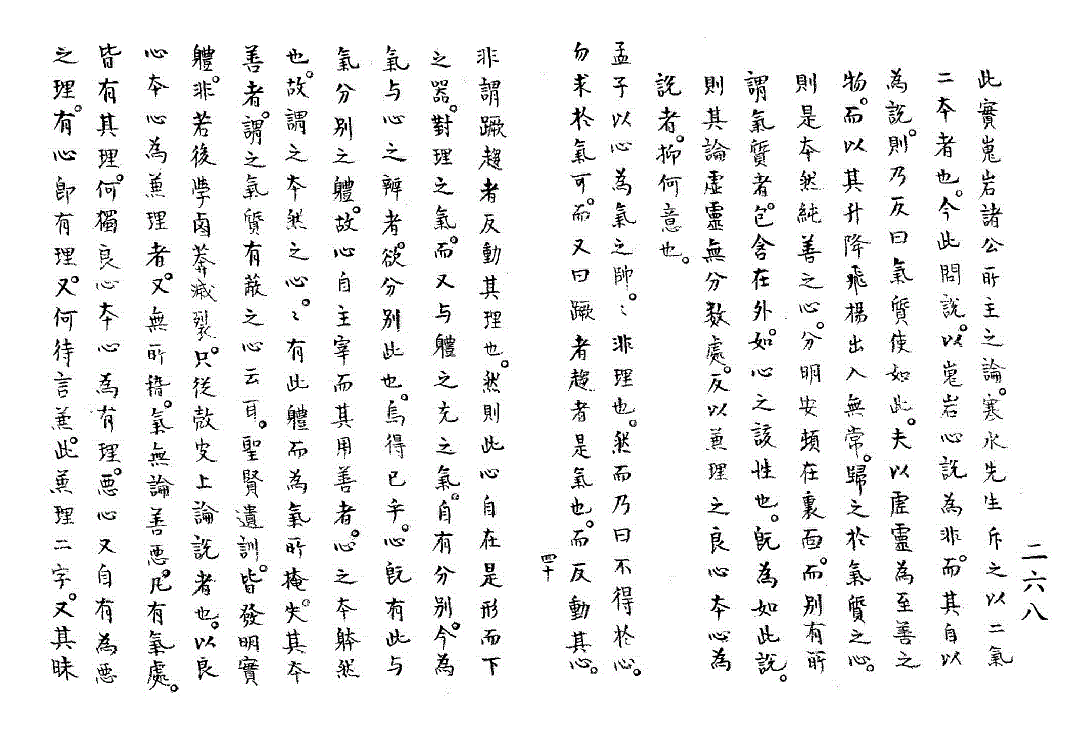 此实嵬岩诸公所主之论。寒水先生斥之以二气二本者也。今此问说。以嵬岩心说为非。而其自以为说。则乃反曰气质使如此。夫以虚灵为至善之物。而以其升降飞扬出入无常。归之于气质之心。则是本然纯善之心。分明安顿在里面。而别有所谓气质者。包含在外。如心之该性也。既为如此说。则其论虚灵无分数处。反以兼理之良心本心为说者。抑何意也。
此实嵬岩诸公所主之论。寒水先生斥之以二气二本者也。今此问说。以嵬岩心说为非。而其自以为说。则乃反曰气质使如此。夫以虚灵为至善之物。而以其升降飞扬出入无常。归之于气质之心。则是本然纯善之心。分明安顿在里面。而别有所谓气质者。包含在外。如心之该性也。既为如此说。则其论虚灵无分数处。反以兼理之良心本心为说者。抑何意也。孟子以心为气之帅。帅非理也。然而乃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而又曰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非谓蹶趋者反动其理也。然则此心自在是形而下之器。对理之气。而又与体之充之气。自有分别。今为气与心之辨者。欲分别此也。乌得已乎。心既有此与气分别之体。故心自主宰而其用善者。心之本体然也。故谓之本然之心。心有此体而为气所掩。失其本善者。谓之气质有蔽之心云耳。圣贤遗训。皆发明实体。非若后学卤莽灭裂。只从壳皮上论说者也。以良心本心为兼理者。又无所稽。气无论善恶。凡有气处。皆有其理。何独良心本心为有理。恶心又自有为恶之理。有心即有理。又何待言兼。此兼理二字。又其昧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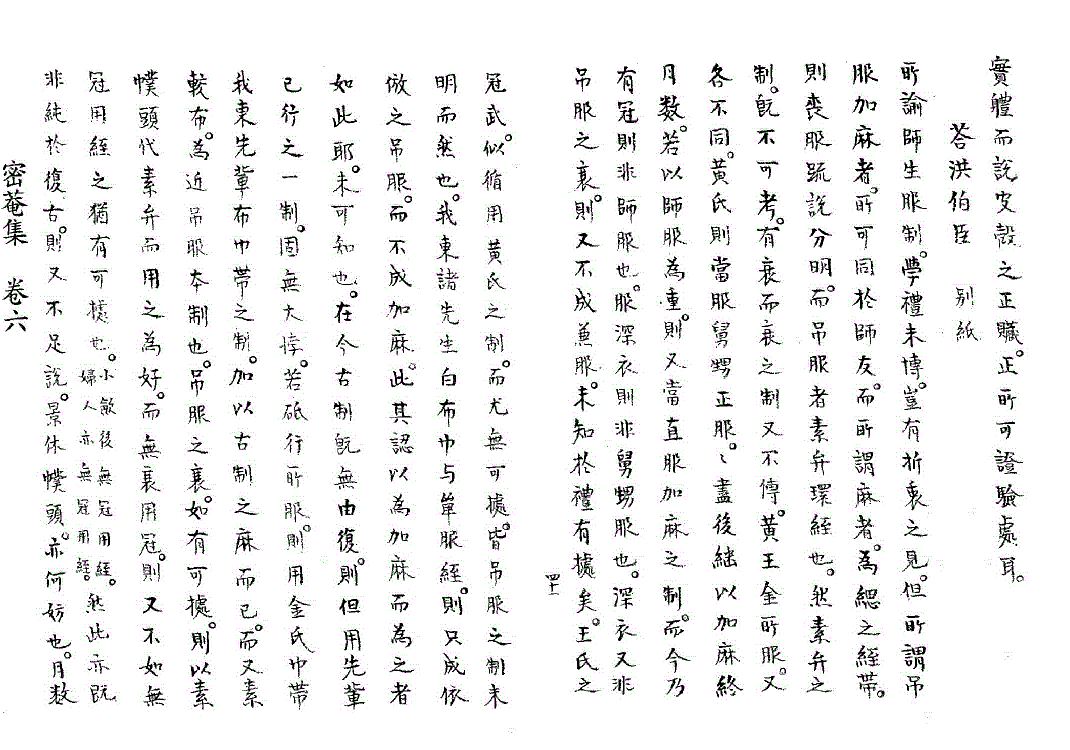 实体而说皮壳之正赃。正所可證验处耳。
实体而说皮壳之正赃。正所可證验处耳。答洪伯臣(别纸)
所谕师生服制。学礼未博。岂有折衷之见。但所谓吊服加麻者。所可同于师友。而所谓麻者。为缌之绖带。则丧服疏说分明。而吊服者素弁环绖也。然素弁之制。既不可考。有衰而衰之制又不传。黄王金所服。又各不同。黄氏则当服舅甥正服。服尽后继以加麻终月数。若以师服为重。则又当直服加麻之制。而今乃有冠则非师服也。服深衣则非舅甥服也。深衣又非吊服之衰。则又不成兼服。未知于礼有据矣。王氏之冠武。似循用黄氏之制。而尤无可据。皆吊服之制未明而然也。我东诸先生白布巾与单服绖。则只成依仿之吊服。而不成加麻。此其认以为加麻而为之者如此耶。未可知也。在今古制既无由复。则但用先辈已行之一制。固无大悖。若砥行所服。则用金氏巾带我东先辈布巾带之制。加以古制之麻而已。而又素较布。为近吊服本制也。吊服之衰。如有可据。则以素幞头代素弁而用之为好。而无衰用冠。则又不如无冠用绖之犹有可据也。(小敛后无冠用绖。妇人亦无冠用绖。)然此亦既非纯于复古。则又不足说。景休幞头。亦何妨也。月数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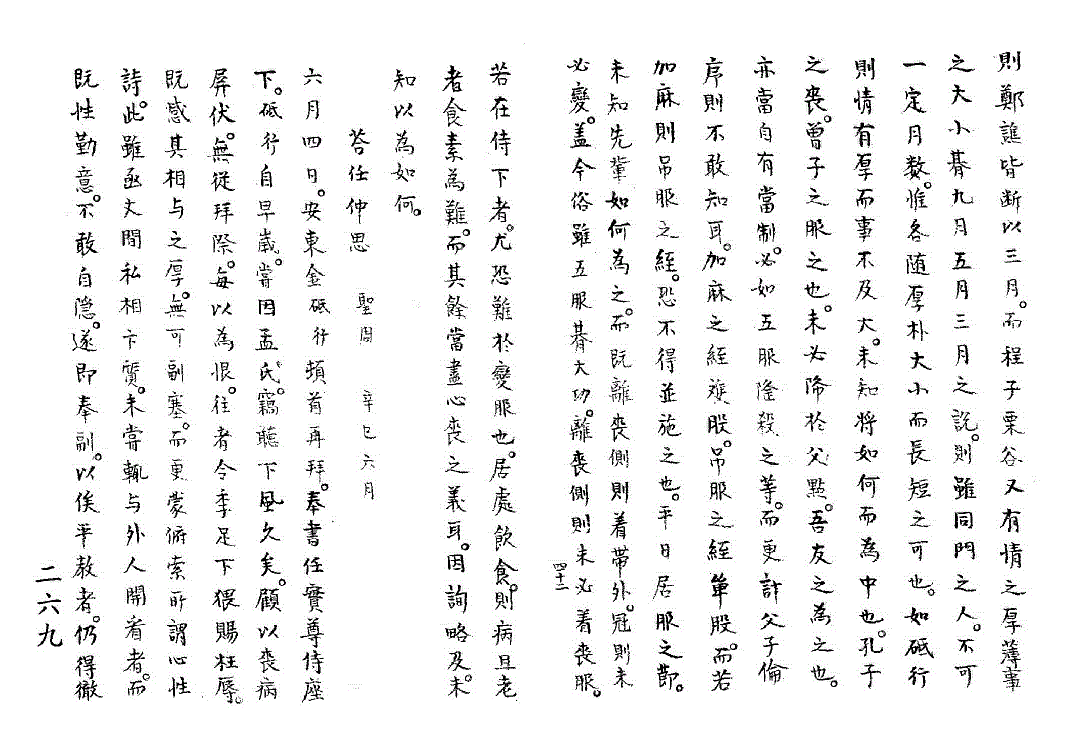 则郑谯皆断以三月。而程子栗谷又有情之厚薄事之大小期九月五月三月之说。则虽同门之人。不可一定月数。惟各随厚朴大小而长短之可也。如砥行则情有厚而事不及大。未知将如何而为中也。孔子之丧。曾子之服之也。未必降于父点。吾友之为之也。亦当自有当制。必如五服隆杀之等。而更计父子伦序则不敢知耳。加麻之绖双股。吊服之绖单股。而若加麻则吊服之绖。恐不得并施之也。平日居服之节。未知先辈如何为之。而既离丧侧则着带外。冠则未必变。盖今俗虽五服期大功。离丧侧则未必着丧服。若在侍下者。尤恐难于变服也。居处饮食。则病且老者食素为难。而其馀当尽心丧之义耳。因询略及。未知以为如何。
则郑谯皆断以三月。而程子栗谷又有情之厚薄事之大小期九月五月三月之说。则虽同门之人。不可一定月数。惟各随厚朴大小而长短之可也。如砥行则情有厚而事不及大。未知将如何而为中也。孔子之丧。曾子之服之也。未必降于父点。吾友之为之也。亦当自有当制。必如五服隆杀之等。而更计父子伦序则不敢知耳。加麻之绖双股。吊服之绖单股。而若加麻则吊服之绖。恐不得并施之也。平日居服之节。未知先辈如何为之。而既离丧侧则着带外。冠则未必变。盖今俗虽五服期大功。离丧侧则未必着丧服。若在侍下者。尤恐难于变服也。居处饮食。则病且老者食素为难。而其馀当尽心丧之义耳。因询略及。未知以为如何。答任仲思(圣周○辛巳六月)
六月四日。安东金砥行顿首再拜。奉书任实尊侍座下。砥行自早岁。尝因孟氏。窃听下风久矣。顾以丧病屏伏。无从拜际。每以为恨。往者令季足下猥赐枉辱。既感其相与之厚。无可副塞。而更蒙俯索所谓心性诗。此虽函丈间私相卞质。未尝辄与外人开看者。而既性勤意。不敢自隐。遂即奉副。以俟平教者。仍得彻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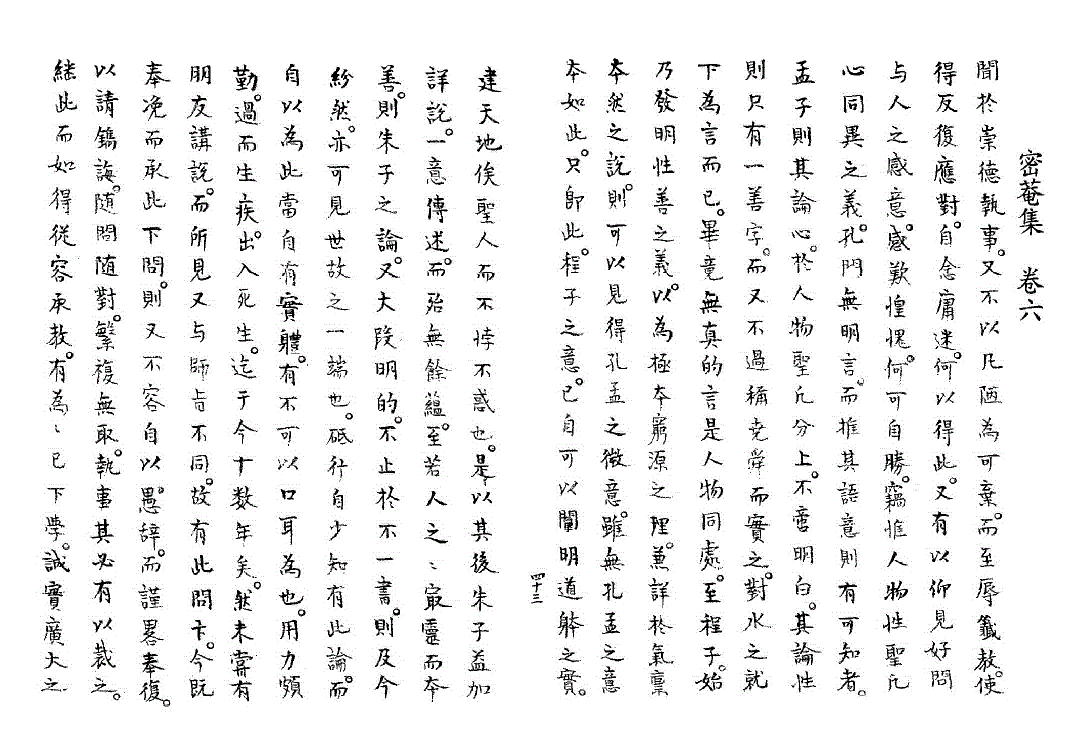 闻于崇德执事。又不以凡陋为可弃。而至辱签教。使得反复应对。自念庸迷。何以得此。又有以仰见好问与人之感意。感叹惶愧。何可自胜。窃惟人物性圣凡心同异之义。孔门无明言。而推其语意则有可知者。孟子则其论心。于人物圣凡分上。不啻明白。其论性则只有一善字。而又不过称尧舜而实之。对水之就下为言而已。毕竟无真的言是人物同处。至程子。始乃发明性善之义。以为极本穷源之理。兼详于气禀本然之说。则可以见得孔孟之微意。虽无孔孟之意本如此。只即此。程子之意。已自可以阐明道体之实。建天地俟圣人而不悖不惑也。是以其后朱子益加详说。一意传述。而殆无馀蕴。至若人之之最灵而本善。则朱子之论。又大段明的。不止于不一书。则及今纷然。亦可见世故之一端也。砥行自少知有此论。而自以为此当自有实体。有不可以口耳为也。用力颇勤。过而生疾。出入死生。迄于今十数年矣。然未尝有朋友讲说。而所见又与师旨不同。故有此问卞。今既奉浼而承此下问。则又不容自以愚辞。而谨略奉复。以请镌诲。随问随对。繁复无取。执事其必有以裁之。继此而如得从容承教。有为为己下学。诚实广大之
闻于崇德执事。又不以凡陋为可弃。而至辱签教。使得反复应对。自念庸迷。何以得此。又有以仰见好问与人之感意。感叹惶愧。何可自胜。窃惟人物性圣凡心同异之义。孔门无明言。而推其语意则有可知者。孟子则其论心。于人物圣凡分上。不啻明白。其论性则只有一善字。而又不过称尧舜而实之。对水之就下为言而已。毕竟无真的言是人物同处。至程子。始乃发明性善之义。以为极本穷源之理。兼详于气禀本然之说。则可以见得孔孟之微意。虽无孔孟之意本如此。只即此。程子之意。已自可以阐明道体之实。建天地俟圣人而不悖不惑也。是以其后朱子益加详说。一意传述。而殆无馀蕴。至若人之之最灵而本善。则朱子之论。又大段明的。不止于不一书。则及今纷然。亦可见世故之一端也。砥行自少知有此论。而自以为此当自有实体。有不可以口耳为也。用力颇勤。过而生疾。出入死生。迄于今十数年矣。然未尝有朋友讲说。而所见又与师旨不同。故有此问卞。今既奉浼而承此下问。则又不容自以愚辞。而谨略奉复。以请镌诲。随问随对。繁复无取。执事其必有以裁之。继此而如得从容承教。有为为己下学。诚实广大之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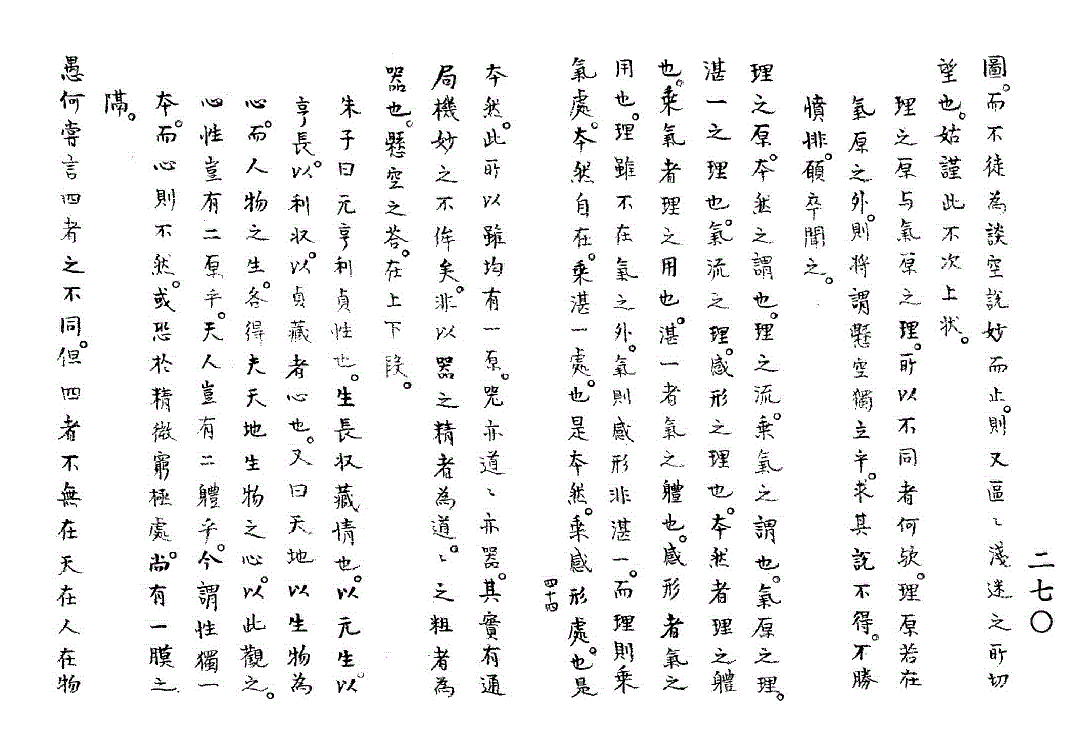 图。而不徒为谈空说妙而止。则又区区浅迷之所切望也。姑谨此不次上状。
图。而不徒为谈空说妙而止。则又区区浅迷之所切望也。姑谨此不次上状。理之原与气原之理。所以不同者何欤。理原若在气原之外。则将谓悬空独立乎。求其说不得。不胜愤悱。愿卒闻之。
理之原。本然之谓也。理之流。乘气之谓也。气原之理。湛一之理也。气流之理。感形之理也。本然者理之体也。乘气者理之用也。湛一者气之体也。感形者气之用也。理虽不在气之外。气则感形非湛一。而理则乘气处。本然自在。乘湛一处。也是本然。乘感形处。也是本然。此所以虽均有一原。器亦道道亦器。其实有通局机妙之不侔矣。非以器之精者为道。道之粗者为器也。悬空之答。在上下段。
朱子曰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此观之。心性岂有二原乎。天人岂有二体乎。今谓性独一本。而心则不然。或恐于精微穷极处。尚有一膜之隔。
愚何尝言四者之不同。但四者不无在天在人在物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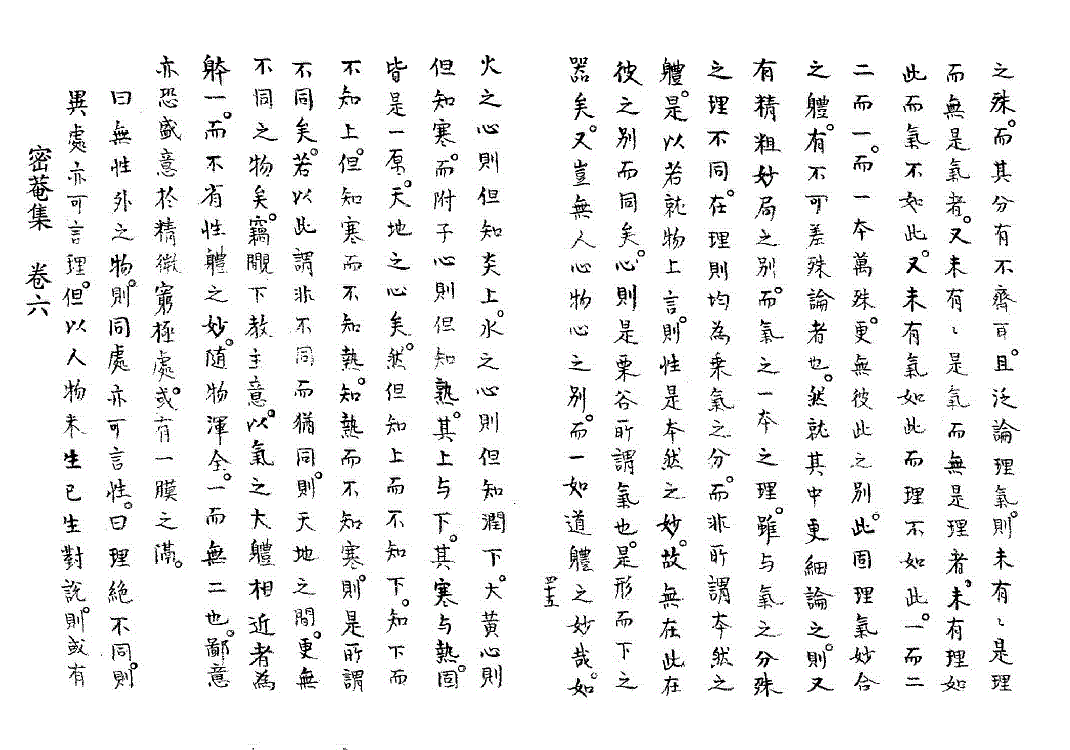 之殊。而其分有不齐耳。且泛论理气。则未有有是理而无是气者。又未有有是气而无是理者。未有理如此而气不如此。又未有气如此而理不如此。一而二二而一。而一本万殊。更无彼此之别。此固理气妙合之体。有不可差殊论者也。然就其中更细论之。则又有精粗妙局之别。而气之一本之理。虽与气之分殊之理不同。在理则均为乘气之分。而非所谓本然之体。是以若就物上言。则性是本然之妙。故无在此在彼之别而同矣。心则是栗谷所谓气也。是形而下之器矣。又岂无人心物心之别。而一如道体之妙哉。如火之心则但知炎上。水之心则但知润下。大黄心则但知寒。而附子心则但知熟。其上与下。其寒与热。固皆是一原。天地之心矣。然但知上而不知下。知下而不知上。但知寒而不知热。知热而不知寒。则是所谓不同矣。若以此谓非不同而犹同。则天地之间。更无不同之物矣。窃覸下教主意。以气之大体相近者为体一。而不省性体之妙。随物浑全。一而无二也。鄙意亦恐盛意于精微穷极处。或有一膜之隔。
之殊。而其分有不齐耳。且泛论理气。则未有有是理而无是气者。又未有有是气而无是理者。未有理如此而气不如此。又未有气如此而理不如此。一而二二而一。而一本万殊。更无彼此之别。此固理气妙合之体。有不可差殊论者也。然就其中更细论之。则又有精粗妙局之别。而气之一本之理。虽与气之分殊之理不同。在理则均为乘气之分。而非所谓本然之体。是以若就物上言。则性是本然之妙。故无在此在彼之别而同矣。心则是栗谷所谓气也。是形而下之器矣。又岂无人心物心之别。而一如道体之妙哉。如火之心则但知炎上。水之心则但知润下。大黄心则但知寒。而附子心则但知熟。其上与下。其寒与热。固皆是一原。天地之心矣。然但知上而不知下。知下而不知上。但知寒而不知热。知热而不知寒。则是所谓不同矣。若以此谓非不同而犹同。则天地之间。更无不同之物矣。窃覸下教主意。以气之大体相近者为体一。而不省性体之妙。随物浑全。一而无二也。鄙意亦恐盛意于精微穷极处。或有一膜之隔。曰无性外之物。则同处亦可言性。曰理绝不同。则异处亦可言理。但以人物未生已生对说。则或有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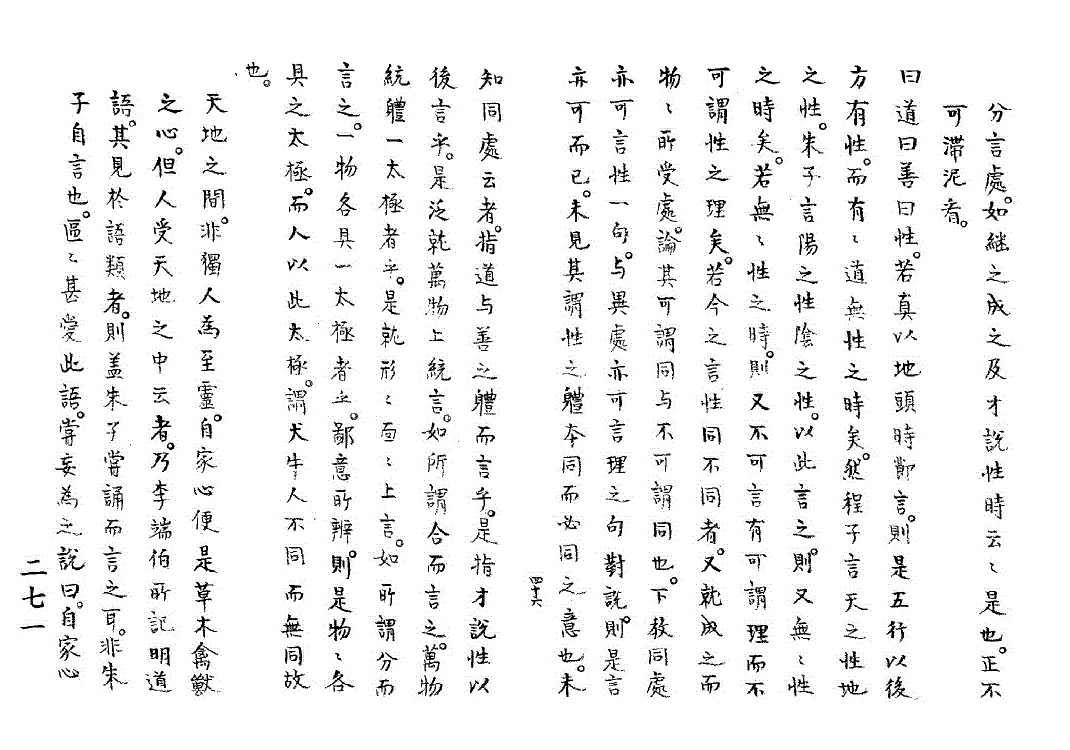 分言处。如继之成之及才说性时云云是也。正不可滞泥看。
分言处。如继之成之及才说性时云云是也。正不可滞泥看。曰道曰善曰性。若真以地头时节言。则是五行以后方有性。而有有道无性之时矣。然程子言天之性地之性。朱子言阳之性阴之性。以此言之。则又无无性之时矣。若无无性之时。则又不可言有可谓理而不可谓性之理矣。若今之言性同不同者。又就成之而物物所受处。论其可谓同与不可谓同也。下教同处亦可言性一句。与异处亦可言理之句对说。则是言亦可而已。未见其谓性之体本同而必同之意也。未知同处云者。指道与善之体而言乎。是指才说性以后言乎。是泛就万物上统言。如所谓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者乎。是就形形面面上言。如所谓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者乎。鄙意所辨。则是物物各具之太极。而人以此太极。谓犬牛人不同而无同故也。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禽兽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云者。乃李端伯所记明道语。其见于语类者。则盖朱子尝诵而言之耳。非朱子自言也。区区甚爱此语。尝妄为之说曰。自家心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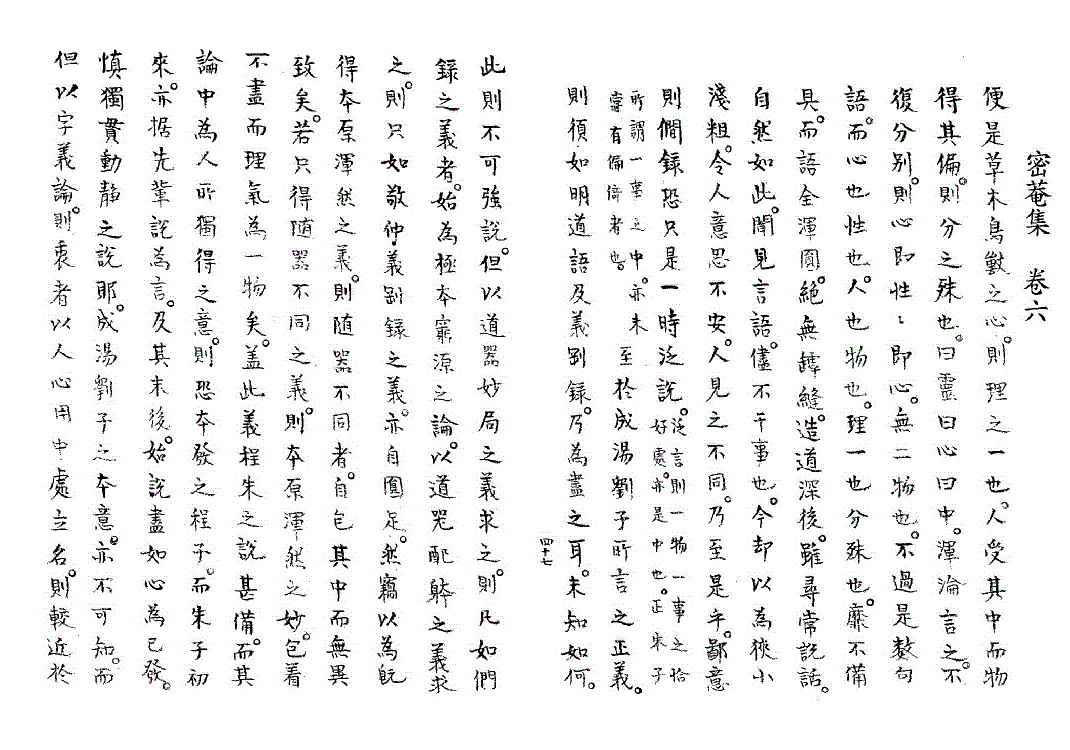 便是草木鸟兽之心。则理之一也。人受其中而物得其偏。则分之殊也。曰灵曰心曰中。浑沦言之。不复分别。则心即性性即心。无二物也。不过是数句语。而心也性也。人也物也。理一也分殊也。靡不备具。而语全浑圆。绝无罅缝。造道深后。虽寻常说话。自然如此。闻见言语。尽不干事也。今却以为狭小浅粗。令人意思不安。人见之不同。乃至是乎。鄙意则僩录恐只是一时泛说。(泛言则一物一事之恰好处。亦是中也。正朱子所谓一事之中。亦未尝有偏倚者也。)至于成汤刘子所言之正义。则须如明道语及义刚录。乃为尽之耳。未知如何。
便是草木鸟兽之心。则理之一也。人受其中而物得其偏。则分之殊也。曰灵曰心曰中。浑沦言之。不复分别。则心即性性即心。无二物也。不过是数句语。而心也性也。人也物也。理一也分殊也。靡不备具。而语全浑圆。绝无罅缝。造道深后。虽寻常说话。自然如此。闻见言语。尽不干事也。今却以为狭小浅粗。令人意思不安。人见之不同。乃至是乎。鄙意则僩录恐只是一时泛说。(泛言则一物一事之恰好处。亦是中也。正朱子所谓一事之中。亦未尝有偏倚者也。)至于成汤刘子所言之正义。则须如明道语及义刚录。乃为尽之耳。未知如何。此则不可强说。但以道器妙局之义求之。则凡如们录之义者。始为极本穷源之论。以道器配体之义求之。则只如敬仲,义刚录之义。亦自圆足。然窃以为既得本原浑然之义。则随器不同者。自包其中而无异致矣。若只得随器不同之义。则本原浑然之妙。包着不尽而理气为一物矣。盖此义程朱之说甚备。而其论中为人所独得之意。则恐本发之程子。而朱子初来。亦据先辈说为言。及其末后。始说尽如心为已发。慎独贯动静之说耶。成汤刘子之本意。亦不可知。而但以字义论。则衷者以人心用中处立名。则较近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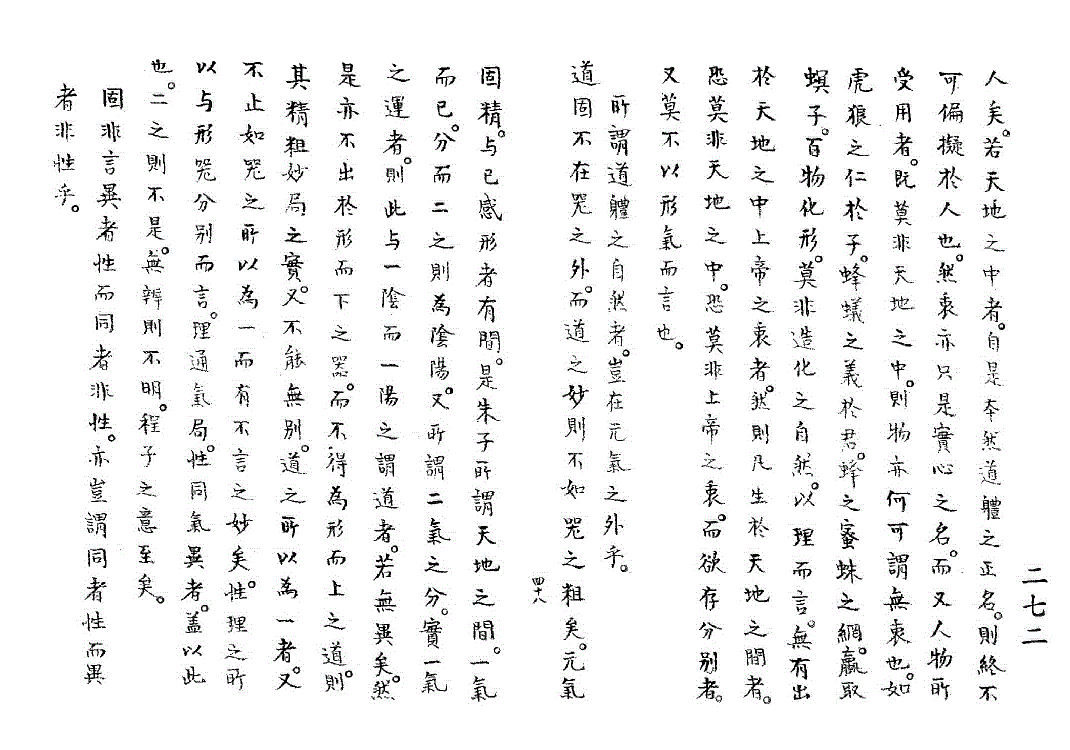 人矣。若天地之中者。自是本然道体之正名。则终不可偏拟于人也。然衷亦只是实心之名。而又人物所受用者。既莫非天地之中。则物亦何可谓无衷也。如虎狼之仁于子。蜂蚁之义于君。蜂之蜜蛛之纲。蠃取螟子。百物化形。莫非造化之自然。以理而言。无有出于天地之中上帝之衷者。然则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恐莫非天地之中。恐莫非上帝之衷。而欲存分别者。又莫不以形气而言也。
人矣。若天地之中者。自是本然道体之正名。则终不可偏拟于人也。然衷亦只是实心之名。而又人物所受用者。既莫非天地之中。则物亦何可谓无衷也。如虎狼之仁于子。蜂蚁之义于君。蜂之蜜蛛之纲。蠃取螟子。百物化形。莫非造化之自然。以理而言。无有出于天地之中上帝之衷者。然则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恐莫非天地之中。恐莫非上帝之衷。而欲存分别者。又莫不以形气而言也。所谓道体之自然者。岂在元气之外乎。
道固不在器之外。而道之妙则不如器之粗矣。元气固精。与已感形者有间。是朱子所谓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二之则为阴阳。又所谓二气之分。实一气之运者。则此与一阴而一阳之谓道者。若无异矣。然是亦不出于形而下之器。而不得为形而上之道。则其精粗妙局之实。又不能无别。道之所以为一者。又不止如器之所以为一而有不言之妙矣。性理之所以与形器分别而言。理通气局。性同气异者。盖以此也。二之则不是。无辨则不明。程子之意至矣。
固非言异者性而同者非性。亦岂谓同者性而异者非性乎。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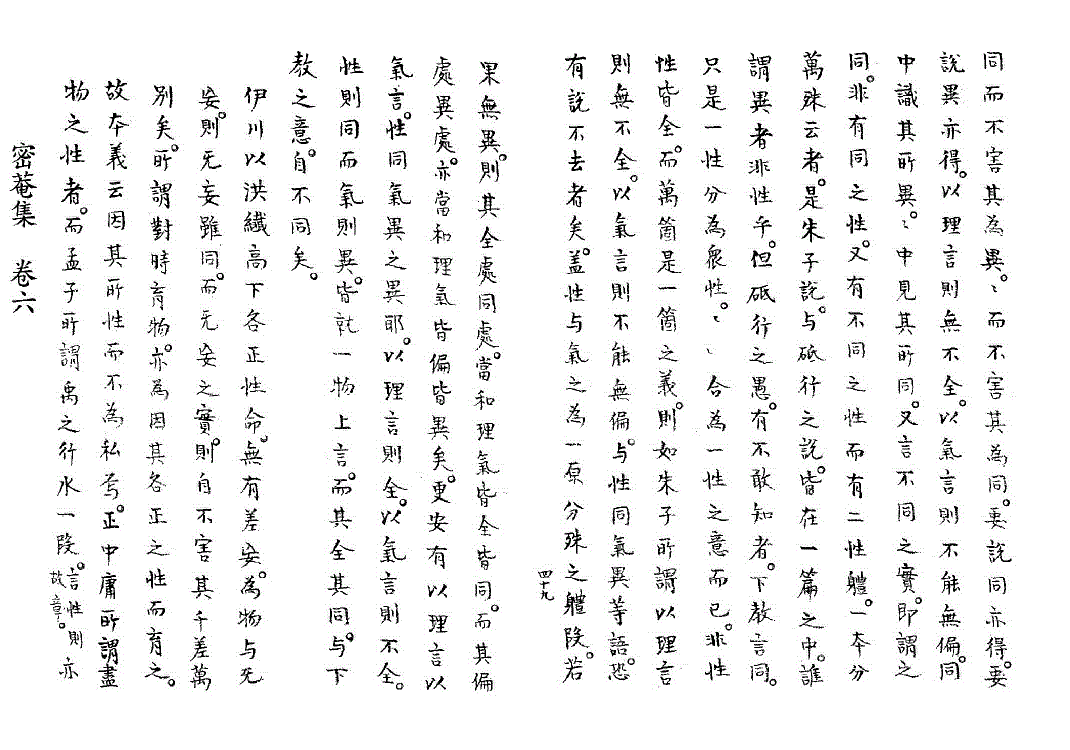 同而不害其为异。异而不害其为同。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以理言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又言不同之实。即谓之同。非有同之性。又有不同之性而有二性体。一本分万殊云者。是朱子说。与砥行之说。皆在一篇之中。谁谓异者非性乎。但砥行之愚。有不耶知者。下教言同。只是一性分为众性。众性合为一性之意而已。非性性皆全。而万个是一个之义。则如朱子所谓以理言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与性同气异等语。恐有说不去者矣。盖性与气之为一原分殊之体段。若果无异。则其全处同处。当和理气皆全皆同。而其偏处异处。亦当和理气皆偏皆异矣。更安有以理言以气言。性同气异之异耶。以理言则全。以气言则不全。性则同而气则异。皆就一物上言。而其全其同。与下教之意。自不同矣。
同而不害其为异。异而不害其为同。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以理言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又言不同之实。即谓之同。非有同之性。又有不同之性而有二性体。一本分万殊云者。是朱子说。与砥行之说。皆在一篇之中。谁谓异者非性乎。但砥行之愚。有不耶知者。下教言同。只是一性分为众性。众性合为一性之意而已。非性性皆全。而万个是一个之义。则如朱子所谓以理言则无不全。以气言则不能无偏。与性同气异等语。恐有说不去者矣。盖性与气之为一原分殊之体段。若果无异。则其全处同处。当和理气皆全皆同。而其偏处异处。亦当和理气皆偏皆异矣。更安有以理言以气言。性同气异之异耶。以理言则全。以气言则不全。性则同而气则异。皆就一物上言。而其全其同。与下教之意。自不同矣。伊川以洪纤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妄。为物与无妄。则无妄虽同。而无妄之实。则自不害其千差万别矣。所谓对时育物。亦为因其各正之性而育之。故本义云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正中庸所谓尽物之性者。而孟子所谓禹之行水一段。(言性则故章。)亦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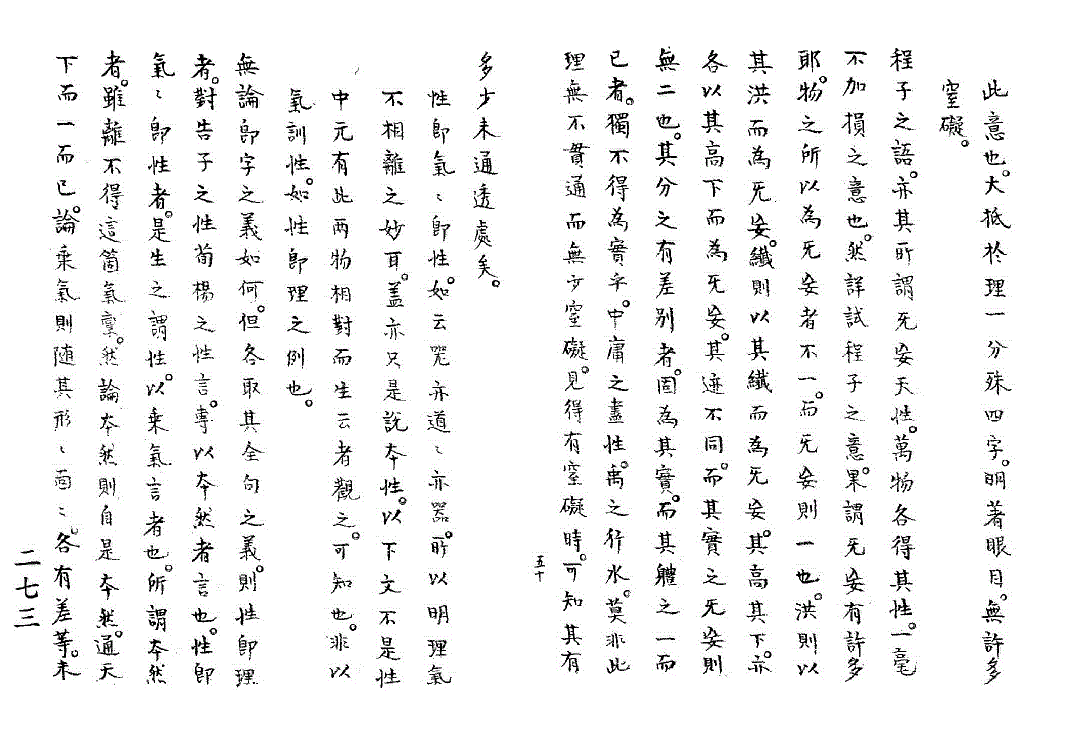 此意也。大抵于理一分殊四字。明著眼目。无许多窒碍。
此意也。大抵于理一分殊四字。明著眼目。无许多窒碍。程子之语。亦其所谓无妄天性。万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损之意也。然详试程子之意。果谓无妄有许多耶。物之所以为无妄者不一。而无妄则一也。洪则以其洪而为无妄。纤则以其纤而为无妄。其高其下。亦各以其高下而为无妄。其迹不同。而其实之无妄则无二也。其分之有差别者。固为其实。而其体之一而已者。独不得为实乎。中庸之尽性。禹之行水。莫非此理无不贯通而无少窒碍。见得有窒碍时。可知其有多少未通透处矣。
性即气气即性。如云器亦道道亦器。所以明理气不相离之妙耳。盖亦只是说本性。以下文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云者观之。可知也。非以气训性。如性即理之例也。
无论即字之义如何。但各取其全句之义。则性即理者。对告子之性荀杨之性言。专以本然者言也。性即气气即性者。是生之谓性。以乘气言者也。所谓本然者。虽离不得这个气禀。然论本然则自是本然。通天下而一而已。论乘气则随其形形面面。各有差等。未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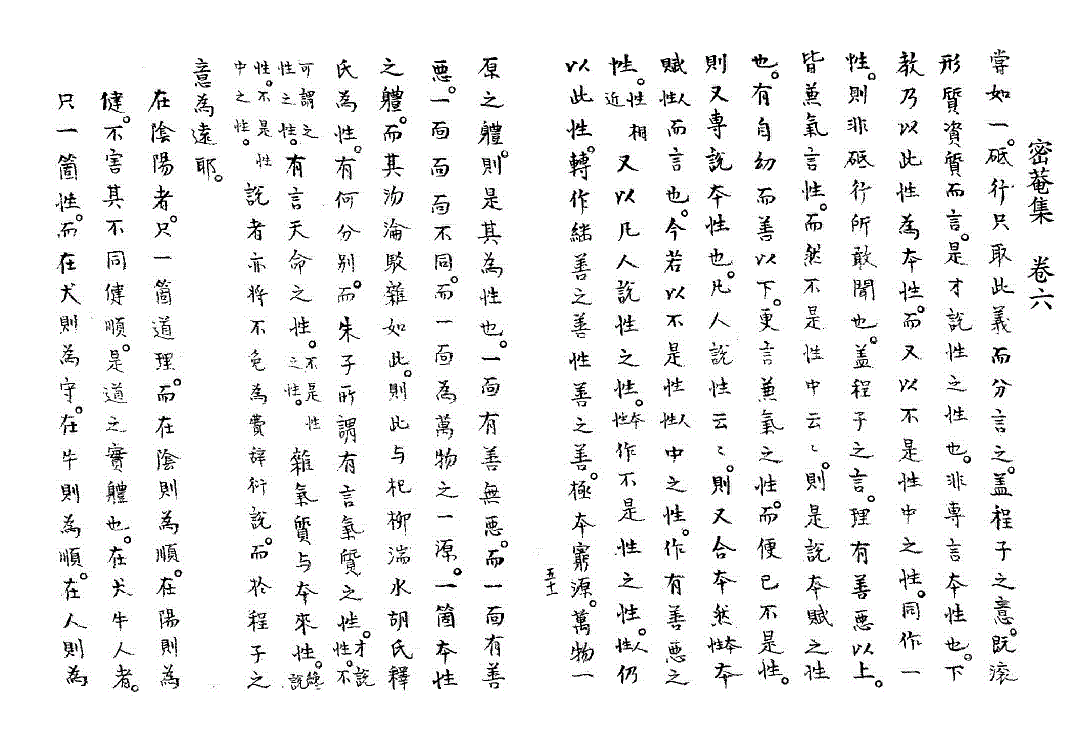 尝如一。砥行只取此义而分言之。盖程子之意。既滚形质资质而言。是才说性之性也。非专言本性也。下教乃以此性为本性。而又以不是性中之性。同作一性。则非砥行所敢闻也。盖程子之言。理有善恶以上。皆兼气言性。而然不是性中云云。则是说本赋之性也。有自幼而善以下。更言兼气之性。而便已不是性。则又专说本性也。凡人说性云云。则又合本然(本性)本赋(人性)而言也。今若以不是性(人性)中之性。作有善恶之性。(性相近)又以凡人说性之性。(本性)作不是性之性。(人性)仍以此性。转作继善之善性善之善。极本穷源。万物一原之体。则是其为性也。一面有善无恶。而一面有善恶。一面面面不同。而一面为万物之一源。一个本性之体。而其沕沦驳杂如此。则此与杞柳湍水胡氏释氏为性。有何分别。而朱子所谓有言气质之性。(才说性。不可谓之性之性。)有言天命之性。(不是性之性。)杂气质与本来性。(才说性。不是性中之性。)说者亦将不免为费辞衍说。而于程子之意为远耶。
尝如一。砥行只取此义而分言之。盖程子之意。既滚形质资质而言。是才说性之性也。非专言本性也。下教乃以此性为本性。而又以不是性中之性。同作一性。则非砥行所敢闻也。盖程子之言。理有善恶以上。皆兼气言性。而然不是性中云云。则是说本赋之性也。有自幼而善以下。更言兼气之性。而便已不是性。则又专说本性也。凡人说性云云。则又合本然(本性)本赋(人性)而言也。今若以不是性(人性)中之性。作有善恶之性。(性相近)又以凡人说性之性。(本性)作不是性之性。(人性)仍以此性。转作继善之善性善之善。极本穷源。万物一原之体。则是其为性也。一面有善无恶。而一面有善恶。一面面面不同。而一面为万物之一源。一个本性之体。而其沕沦驳杂如此。则此与杞柳湍水胡氏释氏为性。有何分别。而朱子所谓有言气质之性。(才说性。不可谓之性之性。)有言天命之性。(不是性之性。)杂气质与本来性。(才说性。不是性中之性。)说者亦将不免为费辞衍说。而于程子之意为远耶。在阴阳者。只一个道理。而在阴则为顺。在阳则为健。不害其不同健顺。是道之实体也。在犬牛人者。只一个性。而在犬则为守。在牛则为顺。在人则为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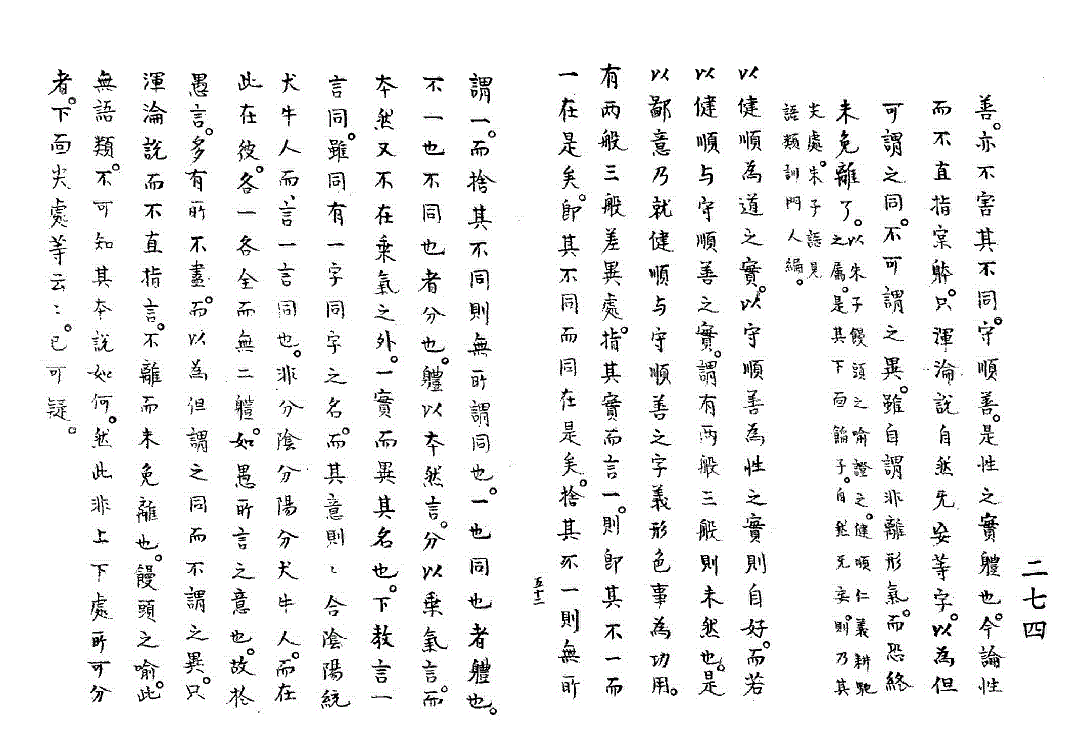 善。亦不害其不同。守顺善。是性之实体也。今论性而不直指宲体。只浑沦说自然无妄等字。以为但可谓之同。不可谓之异。虽自谓非离形气。而恐终未免离了。(以朱子馒头之喻證之。健顺仁义耕驰之属。是其下面馅子。自然无妄。则乃其尖处。朱子语见语类训门人编。)
善。亦不害其不同。守顺善。是性之实体也。今论性而不直指宲体。只浑沦说自然无妄等字。以为但可谓之同。不可谓之异。虽自谓非离形气。而恐终未免离了。(以朱子馒头之喻證之。健顺仁义耕驰之属。是其下面馅子。自然无妄。则乃其尖处。朱子语见语类训门人编。)以健顺为道之实。以守顺善为性之实则自好。而若以健顺与守顺善之实。谓有两般三般则未然也。是以鄙意乃就健顺与守顺善之字义形色事为功用。有两般三般差异处。指其实而言一。则即其不一而一在是矣。即其不同而同在是矣。舍其不一则无所谓一。而舍其不同则无所谓同也。一也同也者体也。不一也不同也者分也。体以本然言。分以乘气言。而本然又不在乘气之外。一实而异其名也。下教言一言同。虽同有一字同字之名。而其意则则合阴阳统犬牛人而言一言同也。非分阴分阳分犬牛人。而在此在彼。各一各全而无二体。如愚所言之意也。故于愚言。多有所不尽。而以为但谓之同而不谓之异。只浑沦说而不直指言。不离而未免离也。馒头之喻。此无语类。不可知其本说如何。然此非上下处所可分者。下面尖处等云云。已可疑。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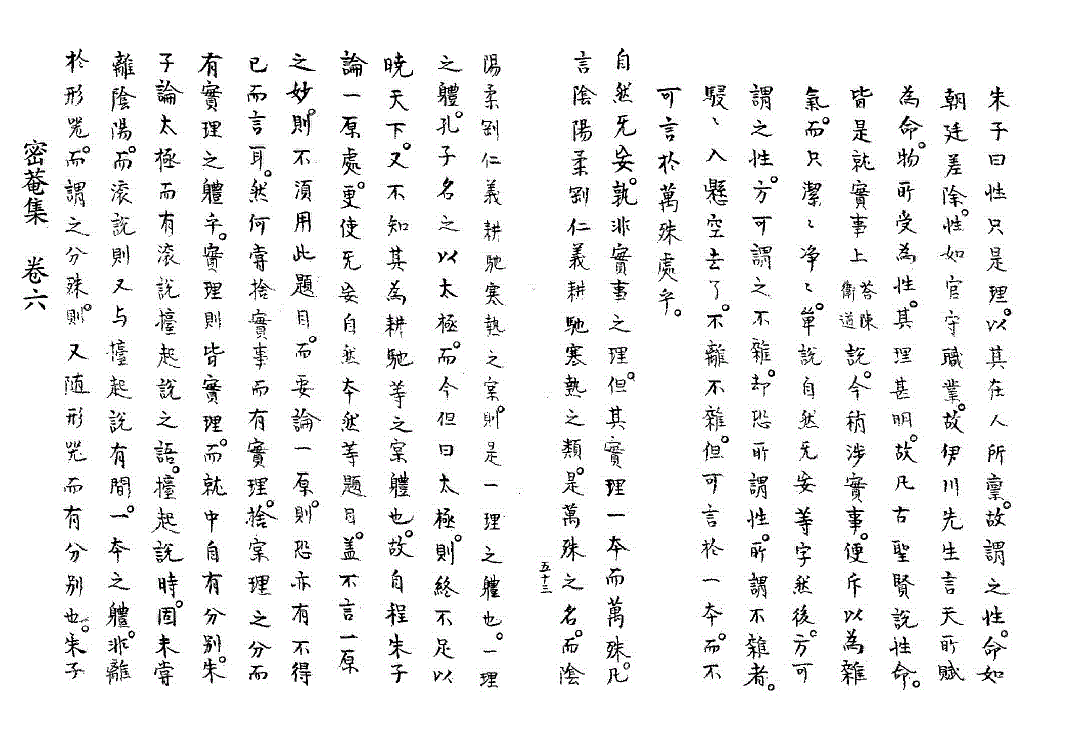 朱子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命如朝廷差除。性如官守职业。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圣贤说性命。皆是就实事上(答陈卫道)说。今稍涉实事。便斥以为杂气。而只洁洁净净。单说自然无妄等字然后。方可谓之性。方可谓之不杂。却恐所谓性。所谓不杂者。骎骎入悬空去了。不离不杂。但可言于一本。而不可言于万殊处乎。
朱子曰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命如朝廷差除。性如官守职业。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圣贤说性命。皆是就实事上(答陈卫道)说。今稍涉实事。便斥以为杂气。而只洁洁净净。单说自然无妄等字然后。方可谓之性。方可谓之不杂。却恐所谓性。所谓不杂者。骎骎入悬空去了。不离不杂。但可言于一本。而不可言于万殊处乎。自然无妄。孰非实事之理。但其实理一本而万殊。凡言阴阳柔刚仁义耕驰寒热之类。是万殊之名。而阴阳柔刚仁义耕驰寒热之宲。则是一理之体也。一理之体。孔子名之以太极。而今但曰太极。则终不足以晚天下。又不知其为耕驰等之宲体也。故自程朱子论一原处。更使无妄自然本然等题目。盖不言一原之妙。则不须用此题目。而要论一原。则恐亦有不得已而言耳。然何尝舍实事而有实理。舍宲理之分而有实理之体乎。实理则皆实理。而就中自有分别。朱子论太极而有滚说抬起说之语。抬起说时。固未尝离阴阳。而滚说则又与抬起说有间。一本之体。非离于形器。而谓之分殊。则又随形器而有分别也。朱子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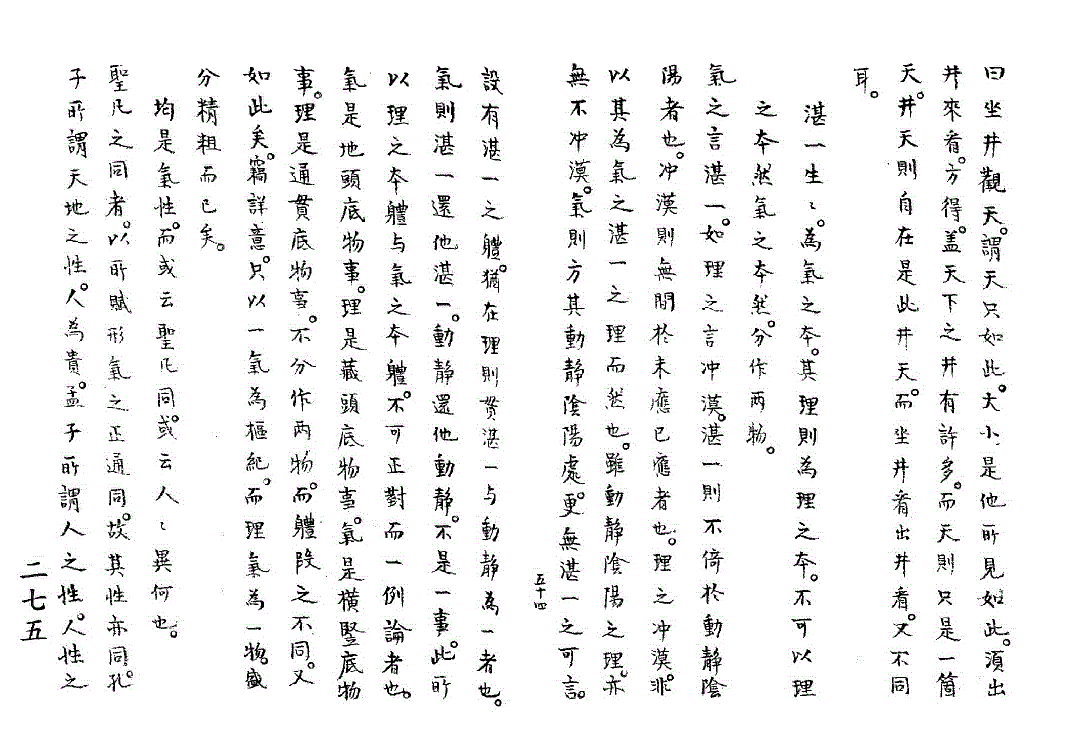 曰坐井观天。谓天只如此。大小是他所见如此。须出井来看。方得。盖天下之井有许多。而天则只是一个天。井天则自在是此井天。而坐井看出井看。又不同耳。
曰坐井观天。谓天只如此。大小是他所见如此。须出井来看。方得。盖天下之井有许多。而天则只是一个天。井天则自在是此井天。而坐井看出井看。又不同耳。湛一生生。为气之本。其理则为理之本。不可以理之本然气之本然。分作两物。
气之言湛一。如理之言冲漠。湛一则不倚于动静阴阳者也。冲漠则无间于未应已应者也。理之冲漠。非以其为气之湛一之理而然也。虽动静阴阳之理。亦无不冲漠。气则方其动静阴阳处。更无湛一之可言。设有湛一之体。犹在理则贯湛一与动静为一者也。气则湛一还他湛一。动静还他动静。不是一事。此所以理之本体与气之本体。不可正对而一例论者也。气是地头底物事。理是藏头底物事。气是横竖底物事。理是通贯底物事。不分作两物。而体段之不同。又如此矣。窃详意。只以一气为枢纪。而理气为一物。盛分精粗而已矣。
均是气性。而或云圣凡同。或云人人异何也。
圣凡之同者。以所赋形气之正通同。故其性亦同。孔子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所谓人之性。人性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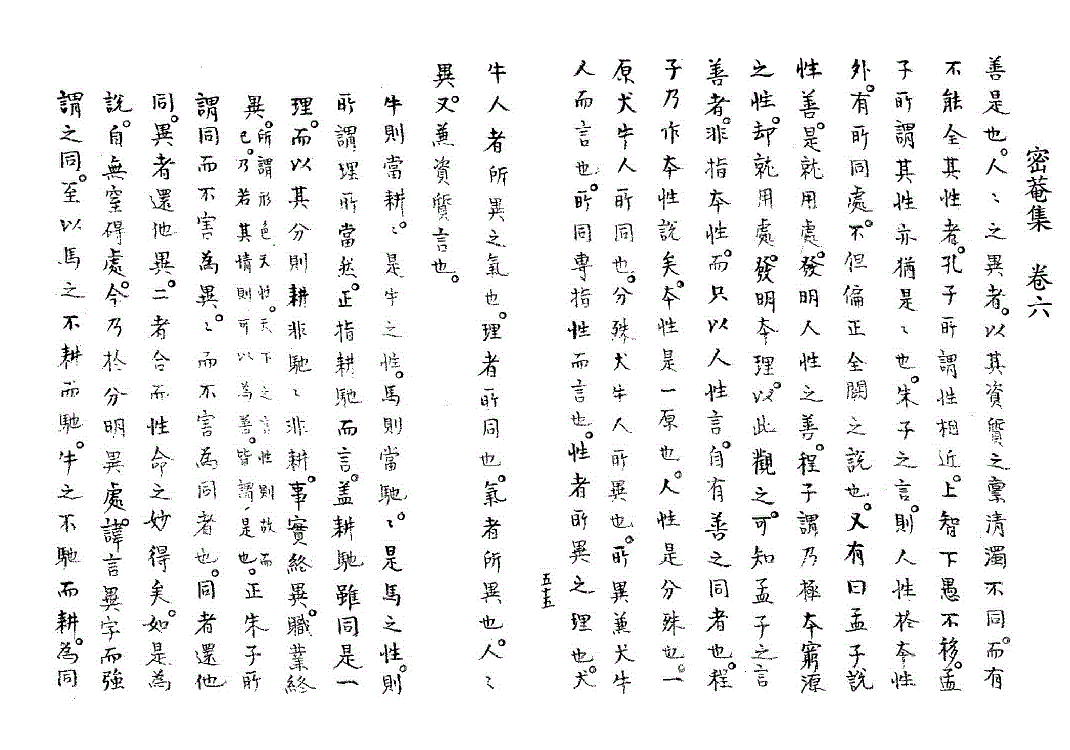 善是也。人人之异者。以其资质之禀清浊不同。而有不能全其性者。孔子所谓性相近。上智下愚不移。孟子所谓其性亦犹是是也。朱子之言。则人性于本性外。有所同处。不但偏正全阙之说也。又有曰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源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以此观之。可知孟子之言善者。非指本性。而只以人性言。自有善之同者也。程子乃作本性说矣。本性是一原也。人性是分殊也。一原犬牛人所同也。分殊犬牛人所异也。所异兼犬牛人而言也。所同专指性而言也。性者所异之理也。犬牛人者所异之气也。理者所同也。气者所异也。人人异。又兼资质言也。
善是也。人人之异者。以其资质之禀清浊不同。而有不能全其性者。孔子所谓性相近。上智下愚不移。孟子所谓其性亦犹是是也。朱子之言。则人性于本性外。有所同处。不但偏正全阙之说也。又有曰孟子说性善。是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谓乃极本穷源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以此观之。可知孟子之言善者。非指本性。而只以人性言。自有善之同者也。程子乃作本性说矣。本性是一原也。人性是分殊也。一原犬牛人所同也。分殊犬牛人所异也。所异兼犬牛人而言也。所同专指性而言也。性者所异之理也。犬牛人者所异之气也。理者所同也。气者所异也。人人异。又兼资质言也。牛则当耕。耕是牛之性。马则当驰。驰是马之性。则所谓理所当然。正指耕驰而言。盖耕驰虽同是一理。而以其分则耕非驰驰非耕。事实终异。职业终 异。(所谓形色天性。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皆谓是也。)正朱子所谓同而不害为异。异而不害为同者也。同者还他同。异者还他异。二者合而性命之妙得矣。如是为说。自无窒碍处。今乃于分明异处。讳言异字而强谓之同。至以马之不耕而驰。牛之不驰而耕。为同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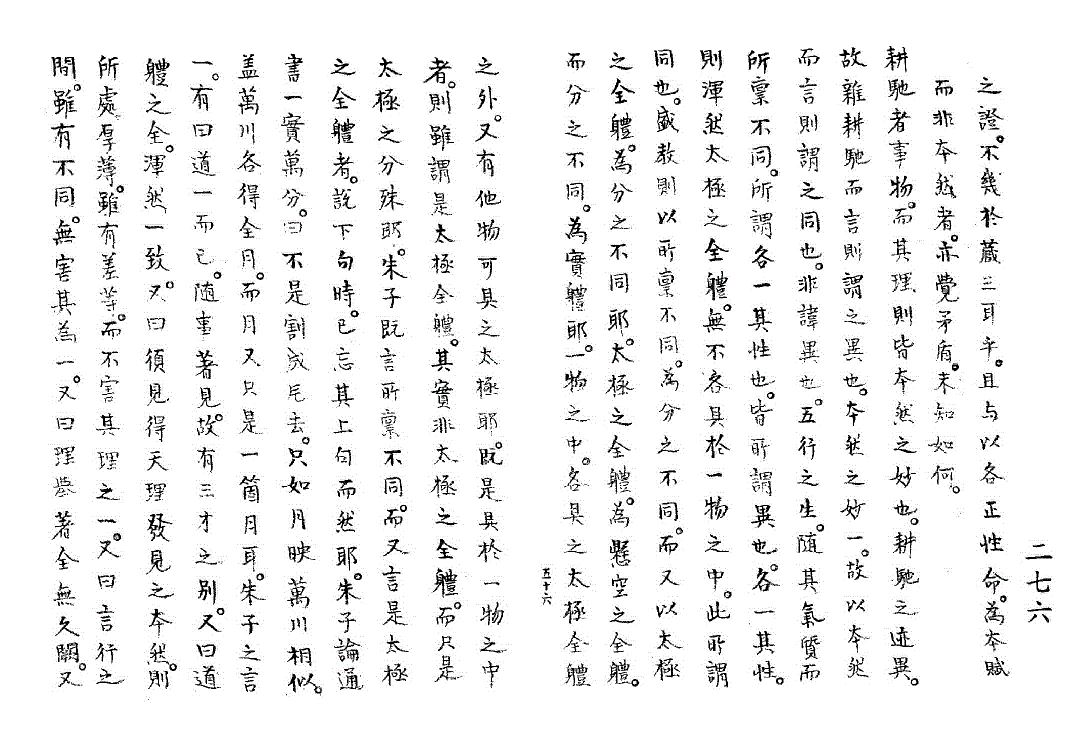 之證。不几于藏三耳乎。且与以各正性命。为本赋而非本然者。亦觉矛盾。未知如何。
之證。不几于藏三耳乎。且与以各正性命。为本赋而非本然者。亦觉矛盾。未知如何。耕驰者事物。而其理则皆本然之妙也。耕驰之迹异。故杂耕驰而言则谓之异也。本然之妙一。故以本然而言则谓之同也。非讳异也。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皆所谓异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此所谓同也。盛教则以所禀不同。为分之不同。而又以太极之全体。为分之不同耶。太极之全体。为悬空之全体。而分之不同。为实体耶。一物之中。各具之太极全体之外。又有他物可具之太极耶。既是具于一物之中者。则虽谓是太极全体。其实非太极之全体。而只是太极之分殊耶。朱子既言所禀不同。而又言是太极之全体者。说下句时。已忘其上句而然耶。朱子论通书一实万分。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万川相似。盖万川各得全月。而月又只是一个月耳。朱子之言一。有曰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又曰道体之全。浑然一致。又曰须见得天理发见之本然。则所处厚薄。虽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又曰言行之间。虽有不同。无害其为一。又曰理举著全无久阙。又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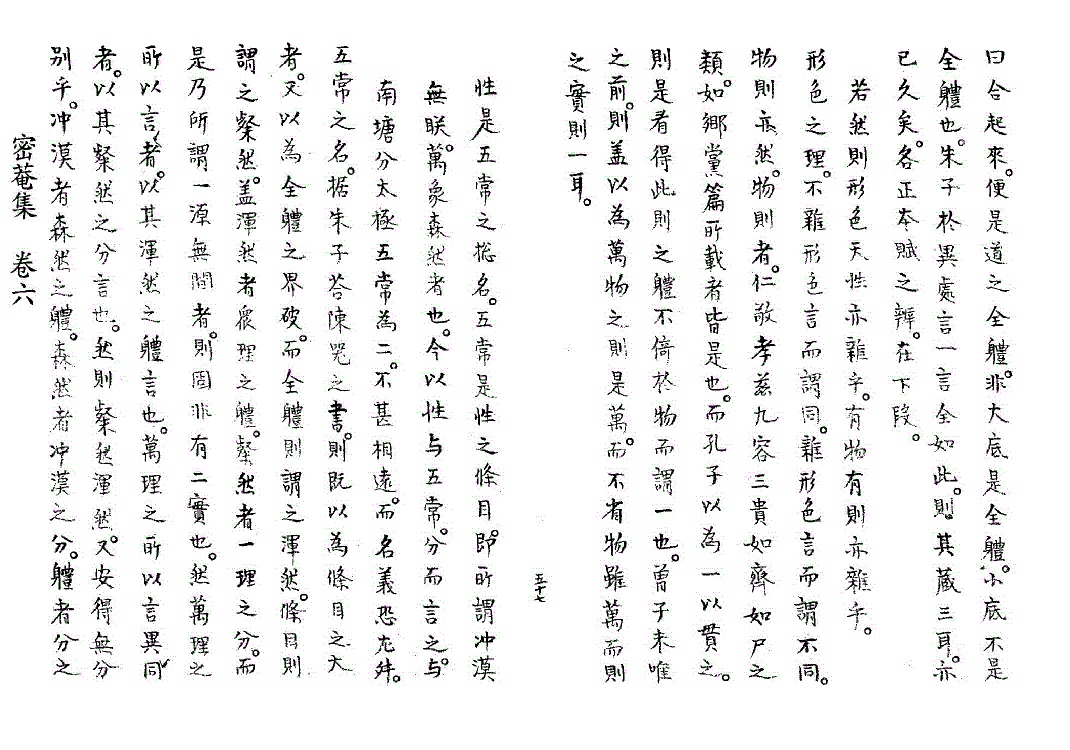 曰合起来。便是道之全体。非大底是全体。小底不是全体也。朱子于异处言一言全如此。则其藏三耳。亦已久矣。各正本赋之辨。在下段。
曰合起来。便是道之全体。非大底是全体。小底不是全体也。朱子于异处言一言全如此。则其藏三耳。亦已久矣。各正本赋之辨。在下段。若然则形色天性亦杂乎。有物有则亦杂乎。
形色之理。不杂形色言而谓同。杂形色言而谓不同。物则亦然。物则者。仁敬孝玆九容三贵如齐如尸之类。如乡党篇所载者皆是也。而孔子以为一以贯之。则是看得此则之体不倚于物而谓一也。曾子未唯之前。则盖以为万物之则是万。而不省物虽万而则之实则一耳。
性是五常之总名。五常是性之条目。即所谓冲漠无眹。万象森然者也。今以性与五常。分而言之。与南塘分太极五常为二。不甚相远。而名义恐尤舛。
五常之名。据朱子答陈器之书。则既以为条目之大者。又以为全体之界破。而全体则谓之浑然。条目则谓之粲然。盖浑然者众理之体。粲然者一理之分。而是乃所谓一源无间者。则固非有二实也。然万理之所以言同者。以其浑然之体言也。万理之所以言异者。以其粲然之分言也。然则粲然浑然。又安得无分别乎。冲漠者森然之体。森然者冲漠之分。体者分之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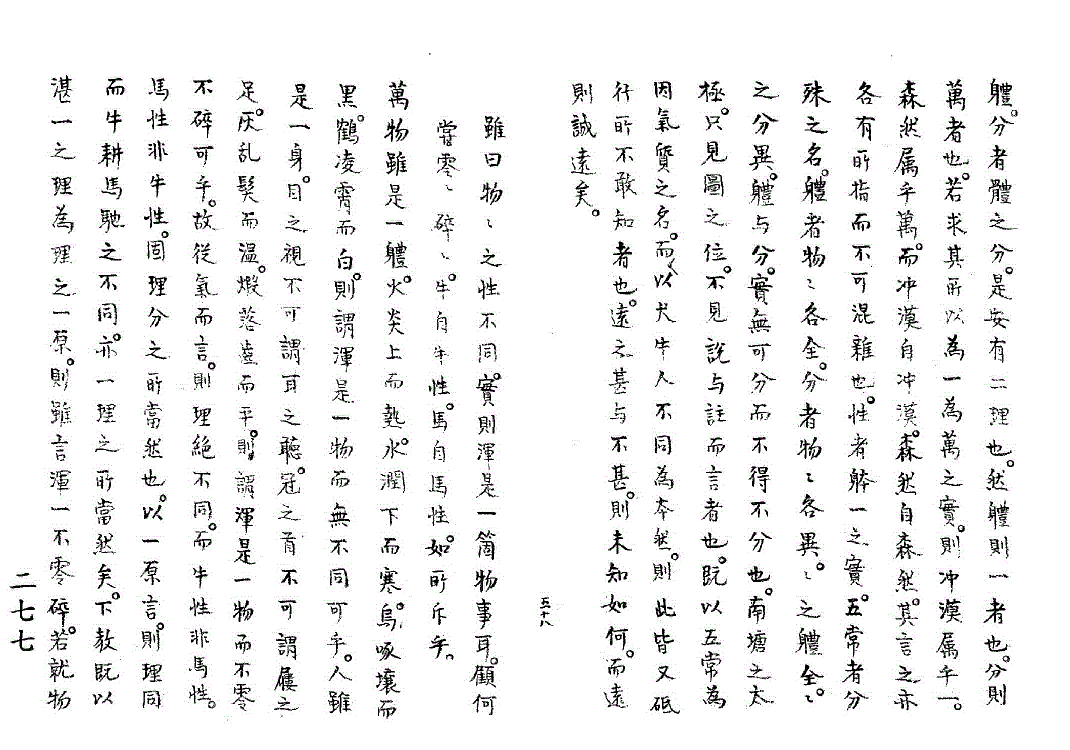 体。分者体之分。是安有二理也。然体则一者也。分则万者也。若求其所以为一为万之实。则冲漠属乎一。森然属乎万。而冲漠自冲漠。森然自森然。其言之亦各有所指而不可混杂也。性者体一之实。五常者分殊之名。体者物物各全。分者物物各异。异之体全。全之分异。体与分。实无可分而不得不分也。南塘之太极。只见图之位。不见说与注而言者也。既以五常为因气质之名。而又以犬牛人不同为本然。则此皆砥行所不敢知者也。远之甚与不甚。则未知如何。而远则诚远矣。
体。分者体之分。是安有二理也。然体则一者也。分则万者也。若求其所以为一为万之实。则冲漠属乎一。森然属乎万。而冲漠自冲漠。森然自森然。其言之亦各有所指而不可混杂也。性者体一之实。五常者分殊之名。体者物物各全。分者物物各异。异之体全。全之分异。体与分。实无可分而不得不分也。南塘之太极。只见图之位。不见说与注而言者也。既以五常为因气质之名。而又以犬牛人不同为本然。则此皆砥行所不敢知者也。远之甚与不甚。则未知如何。而远则诚远矣。虽曰物物之性不同。实则浑是一个物事耳。顾何尝零零碎碎。牛自牛性。马自马性。如所斥乎。
万物虽是一体。火炎上而热。水润下而寒。乌啄壤而黑。鹤凌霄而白。则谓浑是一物而无不同可乎。人虽是一身。目之视不可谓耳之听。冠之首不可谓屦之足。灰乱发而温。煅落齿而平。则谓浑是一物而不零不碎可乎。故从气而言。则理绝不同。而牛性非马性。马性非牛性。固理分之所当然也。以一原言。则理同而牛耕马驰之不同。亦一理之所当然矣。下教既以湛一之理为理之一原。则虽言浑一不零碎。若就物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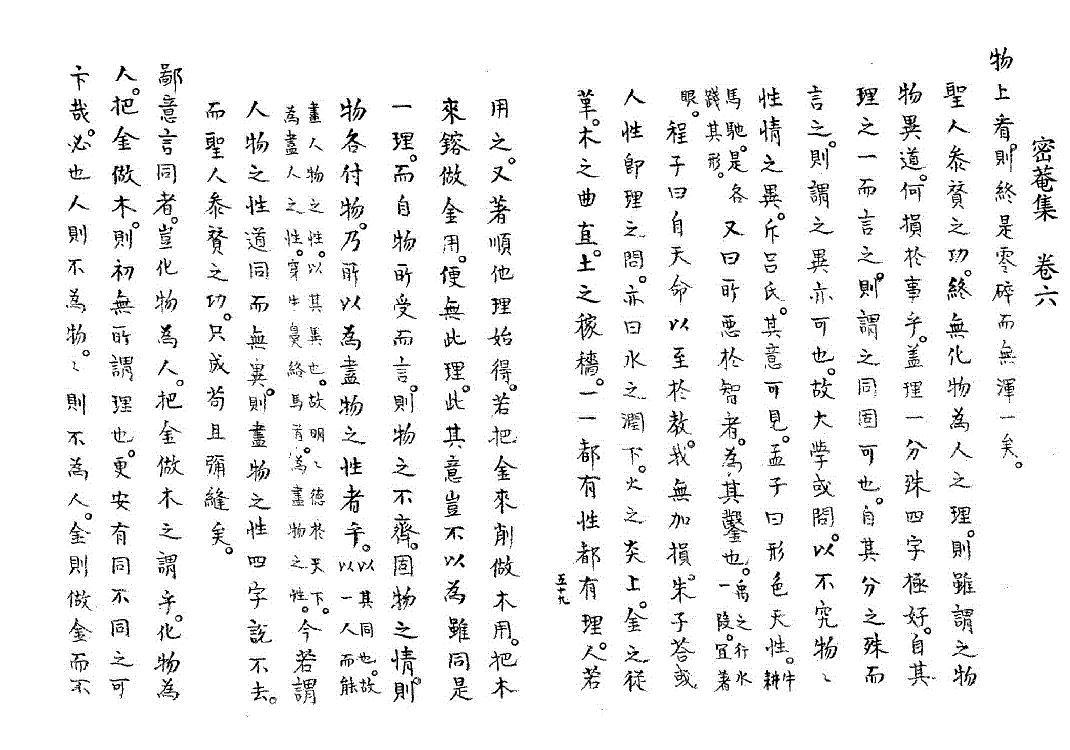 物上看。则终是零碎而无浑一矣。
物上看。则终是零碎而无浑一矣。圣人参赞之功。终无化物为人之理。则虽谓之物物异道。何损于事乎。盖理一分殊四字极好。自其理之一而言之。则谓之同固可也。自其分之殊而言之。则谓之异亦可也。故大学或问。以不究物物性情之异。斥吕氏。其意可见。孟子曰形色天性。(牛耕马驰。是各践其形。)又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禹之行水一段。宜著眼。)程子曰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朱子答或人性即理之问。亦曰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顺他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镕做金用。便无此理。此其意岂不以为虽同是一理。而自物所受而言。则物之不齐。固物之情。则物各付物。乃所以为尽物之性者乎。(以其同也。故以一人而能尽人物之性。以其异也。故明明德于天下。为尽人之性。穿牛鼻络马首。为尽物之性。)今若谓人物之性道同而无异。则尽物之性四字说不去。而圣人参赞之功。只成苟且弥缝矣。
鄙意言同者。岂化物为人。把金做木之谓乎。化物为人。把金做木。则初无所谓理也。更安有同不同之可卞哉。必也人则不为物。物则不为人。金则做金而不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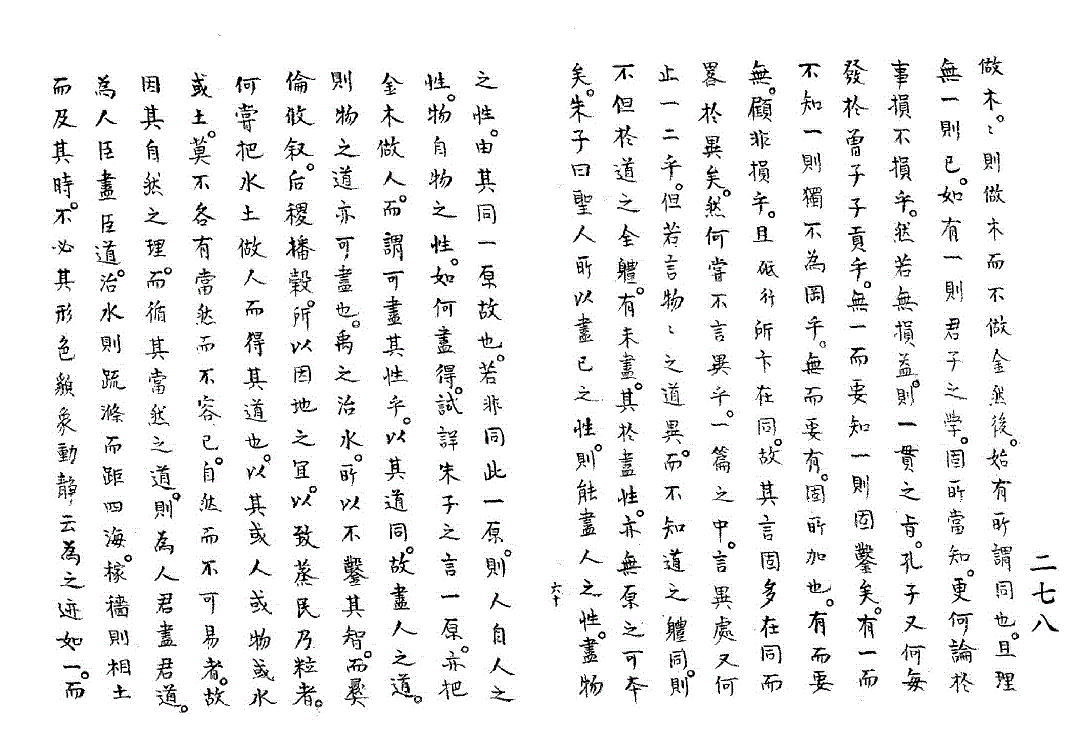 做木。木则牛木而不做金然后。始有所谓同也。且理无一则已。如有一则君子之学。固所当知。更何论于事损不损乎。然若无损益。则一贯之旨。孔子又何每发于曾子子贡乎。无一而要知一则固凿矣。有一而不知一则独不为冈乎。无而要有。固所如也。有而要无。顾非损乎。且砥行所卞在同。故其言固多在同而略于异矣。然何尝不言异乎。一篇之中。言异处又何止一二乎。但若言物物之道异。而不知道之体同。则不但于道之全体。有未尽。其于尽性。亦无原之可本矣。朱子曰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试详朱子之言一原。亦把金木做人。而谓可尽其性乎。以其道同。故尽人之道。则物之道亦可尽也。禹之治水。所以不凿其智。而彝伦攸叙。后稷播谷。所以因地之宜。以致蒸民乃粒者。何尝把水土做人而得其道也。以其或人或物或水或土。莫不各有当然而不容已。自然而不可易者。故因其自然之理。而循其当然之道。则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治水则疏涤而距四海。稼穑则相土而及其时。不必其形色貌象动静云为之迹如一。而
做木。木则牛木而不做金然后。始有所谓同也。且理无一则已。如有一则君子之学。固所当知。更何论于事损不损乎。然若无损益。则一贯之旨。孔子又何每发于曾子子贡乎。无一而要知一则固凿矣。有一而不知一则独不为冈乎。无而要有。固所如也。有而要无。顾非损乎。且砥行所卞在同。故其言固多在同而略于异矣。然何尝不言异乎。一篇之中。言异处又何止一二乎。但若言物物之道异。而不知道之体同。则不但于道之全体。有未尽。其于尽性。亦无原之可本矣。朱子曰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试详朱子之言一原。亦把金木做人。而谓可尽其性乎。以其道同。故尽人之道。则物之道亦可尽也。禹之治水。所以不凿其智。而彝伦攸叙。后稷播谷。所以因地之宜。以致蒸民乃粒者。何尝把水土做人而得其道也。以其或人或物或水或土。莫不各有当然而不容已。自然而不可易者。故因其自然之理。而循其当然之道。则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治水则疏涤而距四海。稼穑则相土而及其时。不必其形色貌象动静云为之迹如一。而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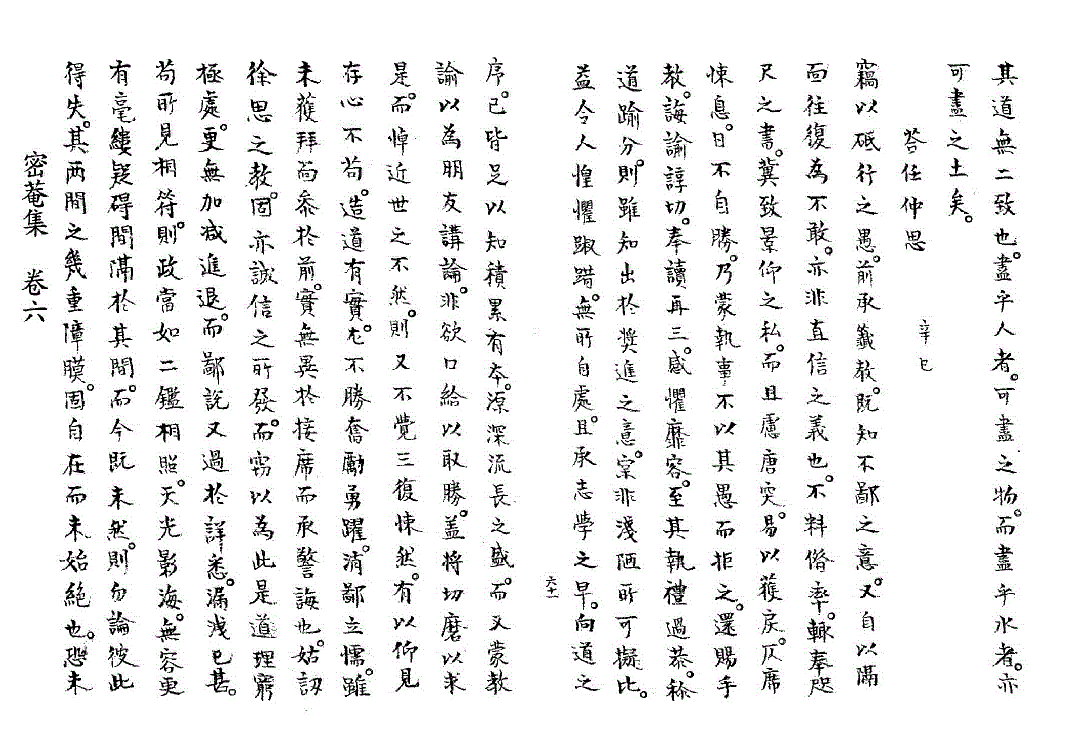 其道无二致也。尽乎人者。可尽之物。而尽乎水者。亦可尽之土矣。
其道无二致也。尽乎人者。可尽之物。而尽乎水者。亦可尽之土矣。答任仲思(辛巳)
窃以砥行之愚。前承签教。既知不鄙之意。又自以隔面往复为不敢。亦非直信之义也。不料僭率。辄奉咫只之书。冀致景仰之私。而且虑唐突。易以获戾。仄席悚息。日不自胜。乃蒙执事不以其愚而拒之。还赐手教。诲谕谆切。奉读再三。感惧靡容。至其执礼过恭。称道踰分。则虽知出于奖进之意。宲非浅陋所可拟比。益令人惶惧踧踖。无所自处。且承志学之早。向道之序。已皆足以知积累有本。源深流长之盛。而又蒙教谕以为明友讲论。非欲口给以取胜。盖将切磨以求是。而悼近世之不然。则又不觉三复悚然。有以仰见存心不苟。造道有实。尤不胜奋励勇跃。消鄙立懦。虽未获拜面参于前。实无异于接席而承警诲也。姑讱徐思之教。固亦诚信之所发。而窃以为此是道理穷极处。更无加减进退。而鄙说又过于详悉。漏泄已甚。苟所见相符。则政当如二鉴相照。天光影海。无容更有毫缕疑碍间隔于其间。而今既未然。则勿论彼此得失。其两间之几重障膜。固自在而未始绝也。恐未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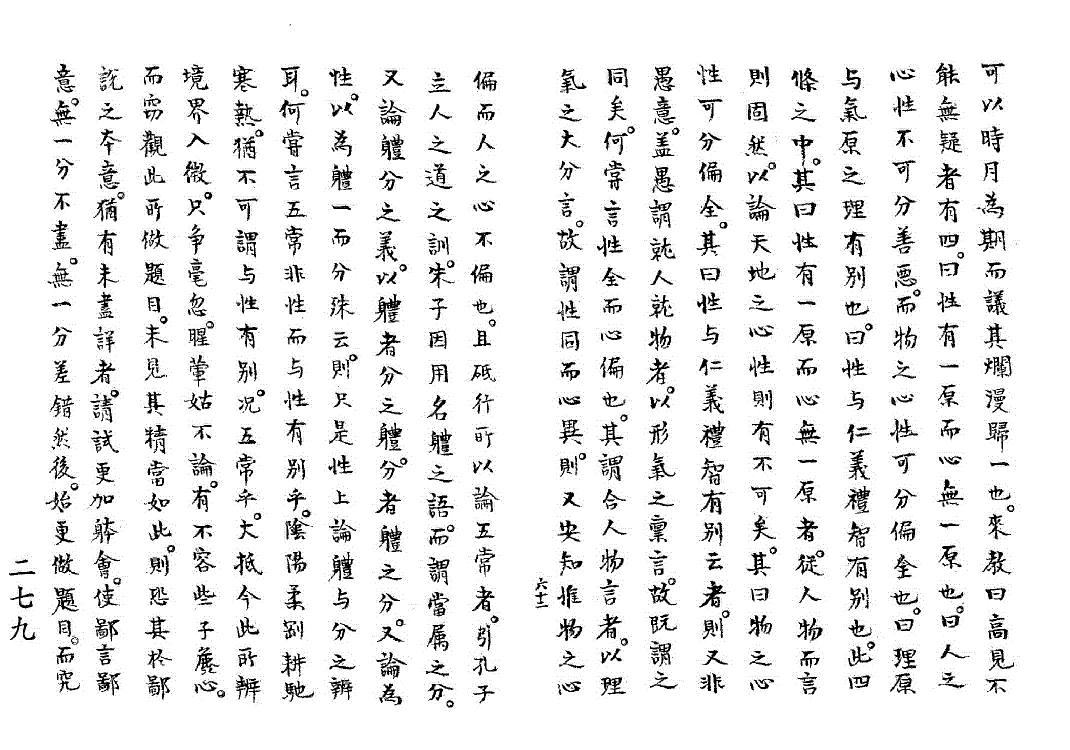 可以时月为期而议其烂漫归一也。来教曰高见不能无疑者有四。曰性有一原而心无一原也。曰人之心性不可分善恶。而物之心性可分偏全也。曰理原与气原之理有别也。曰性与仁义礼智有别也。此四条之中。其曰性有一原而心无一原者。从人物而言则固然。以论天地之心性则有不可矣。其曰物之心性可分偏全。其曰性与仁义礼智有别云者。则又非愚意。盖愚谓就人就物者。以形气之禀言。故既谓之同矣。何尝言性全而心偏也。其谓合人物言者。以理气之大分言。故谓性同而心异。则又安知惟物之心偏而人之心不偏也。且砥行所以论五常者。引孔子立人之道之训。朱子因用名体之语。而谓当属之分。又论体分之义。以体者分之体。分者体之分。又论为性。以为体一而分殊云。则只是性上论体与分之辨耳。何尝言五常非性而与性有别乎。阴阳柔刚耕驰寒热。犹不可谓与性有别。况五常乎。大抵今此所辨境界入微。只争毫忽。腥荤姑不论。有不容些子粗心。而窃观此所做题目。未见其精当如此。则恐其于鄙说之本意。犹有未尽详者。请试更加体会。使鄙言鄙意。无一分不尽。无一分差错然后。始更做题目。而究
可以时月为期而议其烂漫归一也。来教曰高见不能无疑者有四。曰性有一原而心无一原也。曰人之心性不可分善恶。而物之心性可分偏全也。曰理原与气原之理有别也。曰性与仁义礼智有别也。此四条之中。其曰性有一原而心无一原者。从人物而言则固然。以论天地之心性则有不可矣。其曰物之心性可分偏全。其曰性与仁义礼智有别云者。则又非愚意。盖愚谓就人就物者。以形气之禀言。故既谓之同矣。何尝言性全而心偏也。其谓合人物言者。以理气之大分言。故谓性同而心异。则又安知惟物之心偏而人之心不偏也。且砥行所以论五常者。引孔子立人之道之训。朱子因用名体之语。而谓当属之分。又论体分之义。以体者分之体。分者体之分。又论为性。以为体一而分殊云。则只是性上论体与分之辨耳。何尝言五常非性而与性有别乎。阴阳柔刚耕驰寒热。犹不可谓与性有别。况五常乎。大抵今此所辨境界入微。只争毫忽。腥荤姑不论。有不容些子粗心。而窃观此所做题目。未见其精当如此。则恐其于鄙说之本意。犹有未尽详者。请试更加体会。使鄙言鄙意。无一分不尽。无一分差错然后。始更做题目。而究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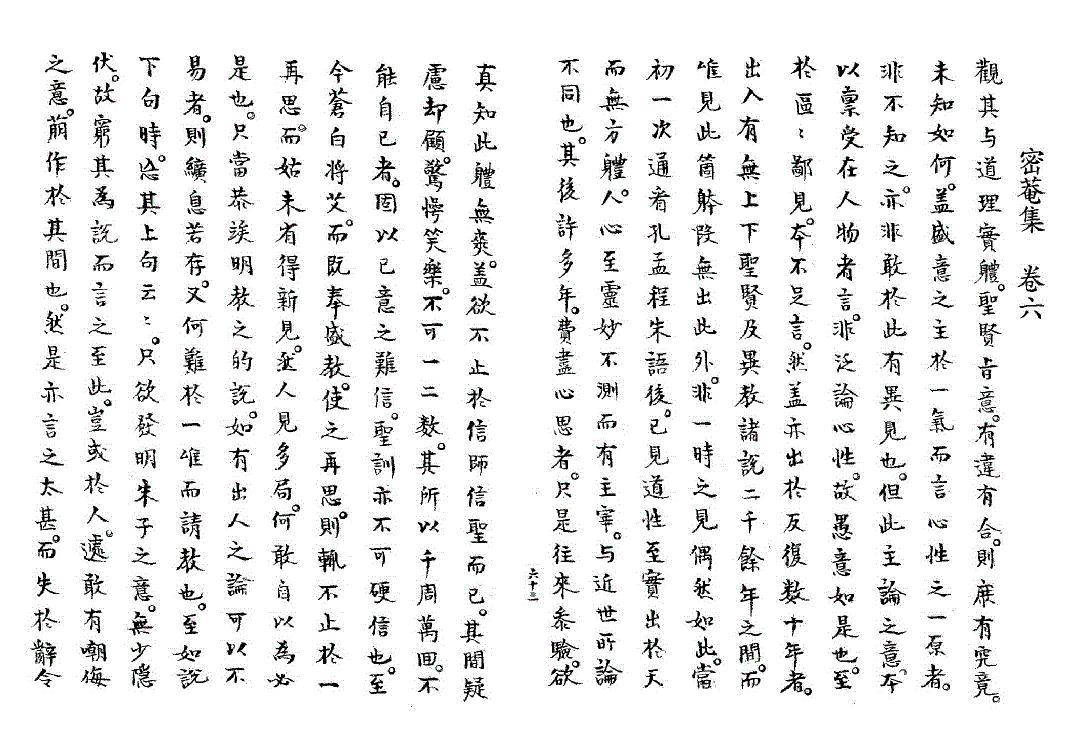 观其与道理实体。圣贤旨意。有违有合。则庶有究竟。未知如何。盖盛意之主于一气而言心性之一原者。非不知之。亦非敢于此有异见也。但此主论之意。本以禀受在人物者言。非泛论心性。故愚意如是也。至于区区鄙见。本不足言。然盖亦出于反复数十年者。出入有无上下圣贤及异教诸说二千馀年之间。而唯见此个体段无出此外。非一时之见偶然如此。当初一次通看孔孟程朱语后。已见道性至实出于天而无方体。人心至灵妙不测而有主宰。与近世所论不同也。其后许多年。费尽心思者。只是往来参验。欲真知此体无爽。盖欲不止于信师信圣而已。其间疑虑却顾。惊愕笑乐。不可一二数。其所以千周万回。不能自已者。固以己意之难信。圣训亦不可硬信也。至今苍白将艾。而既奉盛教。使之再思。则辄不止于一再思。而姑未省得新见。然人见多局。何敢自以为必是也。只当恭俟明教之的说。如有出人之论可以不易者。则纩息若存。又何难于一唯而请教也。至如说下句时。忘其上句云云。只欲发明朱子之意。无少隐伏。故穷其为说而言之至此。岂或于人。遽敢有嘲侮之意。萌作于其间也。然是亦言之太甚。而失于辞令
观其与道理实体。圣贤旨意。有违有合。则庶有究竟。未知如何。盖盛意之主于一气而言心性之一原者。非不知之。亦非敢于此有异见也。但此主论之意。本以禀受在人物者言。非泛论心性。故愚意如是也。至于区区鄙见。本不足言。然盖亦出于反复数十年者。出入有无上下圣贤及异教诸说二千馀年之间。而唯见此个体段无出此外。非一时之见偶然如此。当初一次通看孔孟程朱语后。已见道性至实出于天而无方体。人心至灵妙不测而有主宰。与近世所论不同也。其后许多年。费尽心思者。只是往来参验。欲真知此体无爽。盖欲不止于信师信圣而已。其间疑虑却顾。惊愕笑乐。不可一二数。其所以千周万回。不能自已者。固以己意之难信。圣训亦不可硬信也。至今苍白将艾。而既奉盛教。使之再思。则辄不止于一再思。而姑未省得新见。然人见多局。何敢自以为必是也。只当恭俟明教之的说。如有出人之论可以不易者。则纩息若存。又何难于一唯而请教也。至如说下句时。忘其上句云云。只欲发明朱子之意。无少隐伏。故穷其为说而言之至此。岂或于人。遽敢有嘲侮之意。萌作于其间也。然是亦言之太甚。而失于辞令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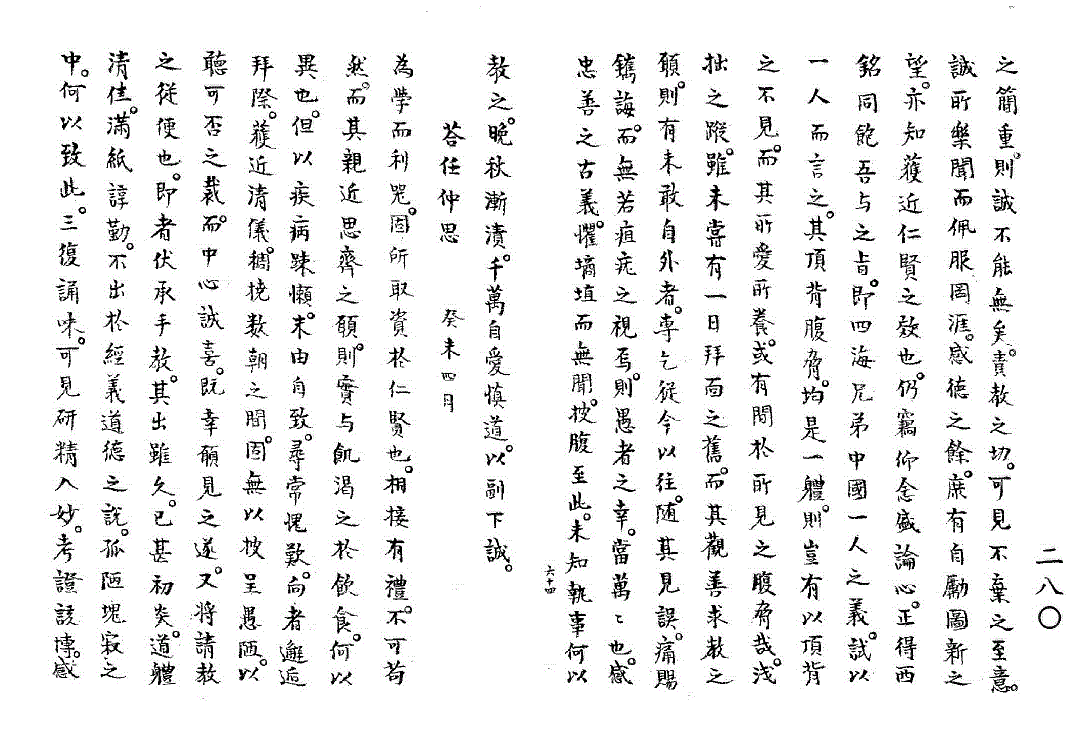 之简重。则诚不能无矣。责教之切。可见不弃之至意。诚所乐闻而佩服罔涯。感德之馀。庶有自励图新之望。亦知获近仁贤之效也。仍窃仰念盛论心。正得西铭同饱吾与之旨。即四海兄弟中国一人之义。试以一人而言之。其顶背腹胁。均是一体。则岂有以顶背之不见。而其所爱所养。或有间于所见之腹胁哉。浅拙之踪。虽未尝有一日拜面之旧。而其观善求教之愿。则有未敢自外者。专乞从今以往。随其见误。痛赐镌(一作镌)诲。而无若疽疣之视焉。则愚者之幸。当万万也。感忠善之古义。惧墑埴而无闻。披腹至此。未知执事何以教之。晚秋渐渍。千万自爱慎道。以副下诚。
之简重。则诚不能无矣。责教之切。可见不弃之至意。诚所乐闻而佩服罔涯。感德之馀。庶有自励图新之望。亦知获近仁贤之效也。仍窃仰念盛论心。正得西铭同饱吾与之旨。即四海兄弟中国一人之义。试以一人而言之。其顶背腹胁。均是一体。则岂有以顶背之不见。而其所爱所养。或有间于所见之腹胁哉。浅拙之踪。虽未尝有一日拜面之旧。而其观善求教之愿。则有未敢自外者。专乞从今以往。随其见误。痛赐镌(一作镌)诲。而无若疽疣之视焉。则愚者之幸。当万万也。感忠善之古义。惧墑埴而无闻。披腹至此。未知执事何以教之。晚秋渐渍。千万自爱慎道。以副下诚。答任仲思(癸未四月)
为学而利器。固所取资于仁贤也。相接有礼。不可苟然。而其亲近思齐之愿。则实与饥渴之于饮食。何以异也。但以疾病疏懒。末由自致。寻常愧叹。向者邂逅拜际。获近清仪。稠挠数朝之间。固无以披呈愚陋。以听可否之裁。而中心诚喜。既幸愿见之遂。又将请教之从便也。即者伏承手教。其出虽久。已甚初炎。道体清佳。满纸谆勤。不出于经义道德之说。孤陋块寂之中。何以致此。三复诵味。可见研精入妙。考證该博。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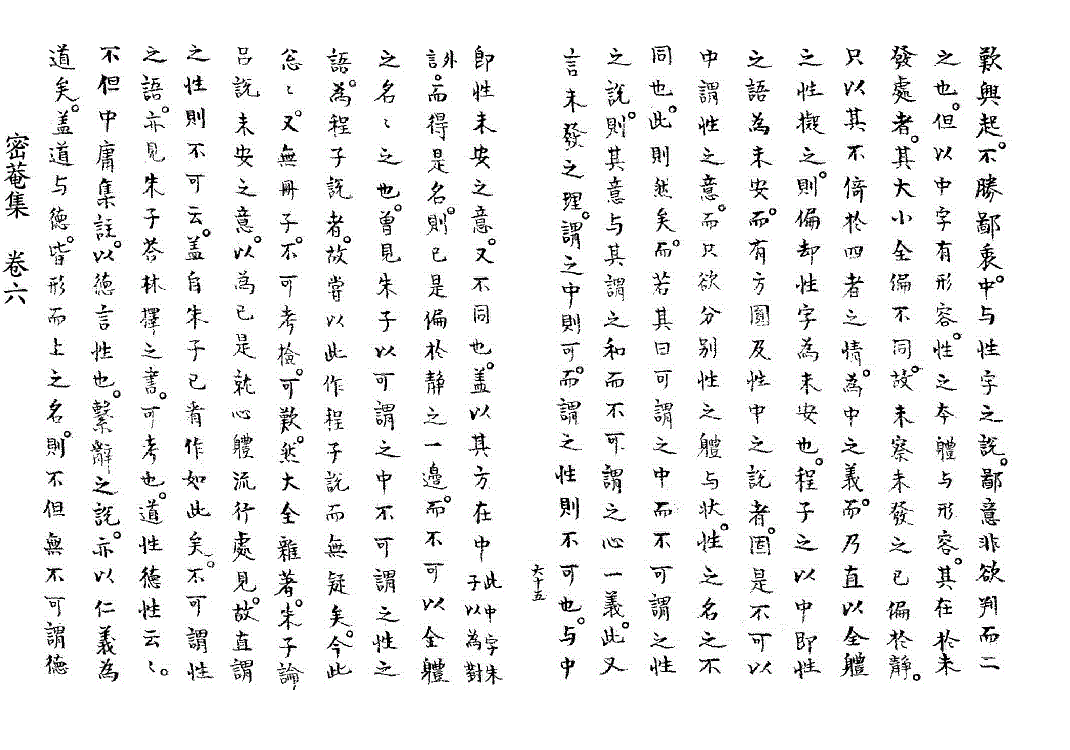 叹兴起。不胜鄙衷。中与性字之说。鄙意非欲判而二之也。但以中字有形容。性之本体与形容。其在于未发处者。其大小全偏不同。故未察未发之已偏于静。只以其不倚于四者之情。为中之义。而乃直以全体之性拟之。则偏却性字为未安也。程子之以中即性之语为未安。而有方圆及性中之说者。固是不可以中谓性之意。而只欲分别性之体与状。性之名之不同也。此则然矣。而若其曰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之说。则其意与其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一义。此又言未发之理。谓之中则可。而谓之性则不可也。与中即性未安之意。又不同也。盖以其方在中(此中字朱子以为对外言。)而得是名。则已是偏于静之一边。而不可以全体之名名之也。曾见朱子以可谓之中不可谓之性之语。为程子说者。故尝以此作程子说而无疑矣。今此匆匆。又无册子。不可考检。可叹。然大全杂著。朱子论吕说未安之意。以为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云。盖自朱子已看作如此矣。不可谓性之语。亦见朱子答林择之书。可考也。道性德性云云。不但中庸集注。以德言性也。系辞之说。亦以仁义为道矣。盖道与德。皆形而上之名。则不但无不可谓德
叹兴起。不胜鄙衷。中与性字之说。鄙意非欲判而二之也。但以中字有形容。性之本体与形容。其在于未发处者。其大小全偏不同。故未察未发之已偏于静。只以其不倚于四者之情。为中之义。而乃直以全体之性拟之。则偏却性字为未安也。程子之以中即性之语为未安。而有方圆及性中之说者。固是不可以中谓性之意。而只欲分别性之体与状。性之名之不同也。此则然矣。而若其曰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之说。则其意与其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一义。此又言未发之理。谓之中则可。而谓之性则不可也。与中即性未安之意。又不同也。盖以其方在中(此中字朱子以为对外言。)而得是名。则已是偏于静之一边。而不可以全体之名名之也。曾见朱子以可谓之中不可谓之性之语。为程子说者。故尝以此作程子说而无疑矣。今此匆匆。又无册子。不可考检。可叹。然大全杂著。朱子论吕说未安之意。以为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云。盖自朱子已看作如此矣。不可谓性之语。亦见朱子答林择之书。可考也。道性德性云云。不但中庸集注。以德言性也。系辞之说。亦以仁义为道矣。盖道与德。皆形而上之名。则不但无不可谓德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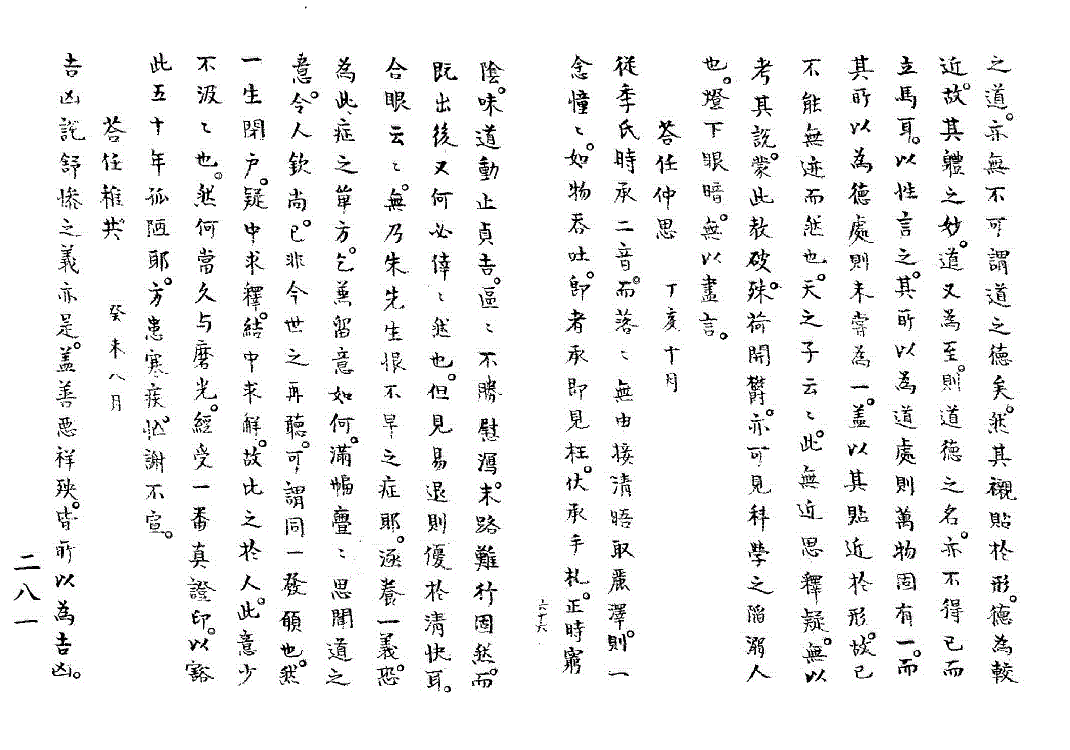 之道。亦无不可谓道之德矣。然其衬贴于形。德为较近。故其体之妙。道又为至。则道德之名。亦不得已而立马耳。以性言之。其所以为道处则万物固有一。而其所以为德处则未尝为一。盖以其贴近于形。故已不能无迹而然也。天之子云云。此无近思释疑。无以考其说。蒙此教破。殊荷开郁。亦可见科学之陷溺人也。灯下眼暗。无以尽言。
之道。亦无不可谓道之德矣。然其衬贴于形。德为较近。故其体之妙。道又为至。则道德之名。亦不得已而立马耳。以性言之。其所以为道处则万物固有一。而其所以为德处则未尝为一。盖以其贴近于形。故已不能无迹而然也。天之子云云。此无近思释疑。无以考其说。蒙此教破。殊荷开郁。亦可见科学之陷溺人也。灯下眼暗。无以尽言。答任仲思(丁亥十月)
从季氏时承二音。而落落无由接清晤取丽泽。则一念憧憧。如物吞吐。即者承即见枉。伏承手札。正时穷阴。味道动止贞吉。区区不胜慰泻。末路难行固然。而既出后又何必倖倖然也。但见易退则优于清快耳。合眼云云。无乃朱先生恨不早之症耶。涵养一义。恐为此症之单方。乞兼留意如何。满幅亹亹思闻道之意。令人钦尚。已非今世之再听。可谓同一发愿也。然一生闭户。疑中求释。结中求解。故比之于人。此意少不汲汲也。然何当久与磨光。经受一番真證印。以豁此五十年孤陋耶。方患寒疾。忙谢不宣。
答任稚共(癸未八月)
吉凶说舒惨之义亦是。盖善恶祥殃。皆所以为吉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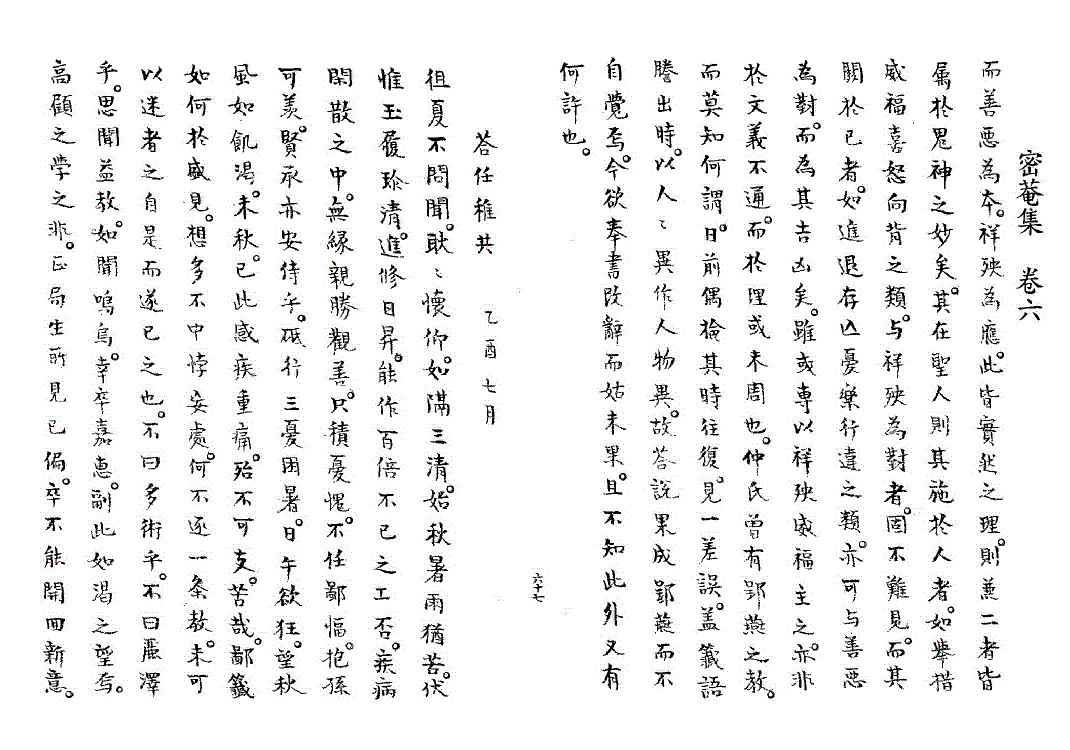 而善恶为本。祥殃为应。此皆实然之理。则兼二者皆属于鬼神之妙矣。其在圣人则其施于人者。如举措威福喜怒向背之类。与祥殃为对者。固不难见。而其关于己者。如进退存亡忧乐行达之类。亦可与善恶为对。而为其吉凶矣。虽或专以祥殃威福主之。亦非于文义不通。而于理或未周也。仲氏曾有郢燕之教。而莫知何谓。日前偶检其时往复。见一差误。盖签语誊出时。以人人异作人物异。故答说果成郢燕而不自觉焉。今欲奉书改辞而姑未果。且不知此外又有何许也。
而善恶为本。祥殃为应。此皆实然之理。则兼二者皆属于鬼神之妙矣。其在圣人则其施于人者。如举措威福喜怒向背之类。与祥殃为对者。固不难见。而其关于己者。如进退存亡忧乐行达之类。亦可与善恶为对。而为其吉凶矣。虽或专以祥殃威福主之。亦非于文义不通。而于理或未周也。仲氏曾有郢燕之教。而莫知何谓。日前偶检其时往复。见一差误。盖签语誊出时。以人人异作人物异。故答说果成郢燕而不自觉焉。今欲奉书改辞而姑未果。且不知此外又有何许也。答任稚共(乙酉七月)
徂夏不问闻。耿耿怀仰。如隔三清。始秋暑雨犹苦。伏惟玉履珍清。进修日升。能作百倍不已之工否。疾病闲散之中。无缘亲胜观善。只积忧愧。不任鄙愊。抱孙可羡。贤承亦安侍乎。砥行三忧困暑。日午欲狂。望秋风如饥渴。未秋。已此感疾重痛。殆不可支。苦哉。鄙签如何于盛见。想多不中悖妄处。何不逐一条教。未可以迷者之自是而遂已之也。不曰多术乎。不曰丽泽乎。思闻益教。如闻呜乌。幸卒嘉惠。副此如渴之望焉。高顾之学之非。正局生所见已偏。卒不能开回新意。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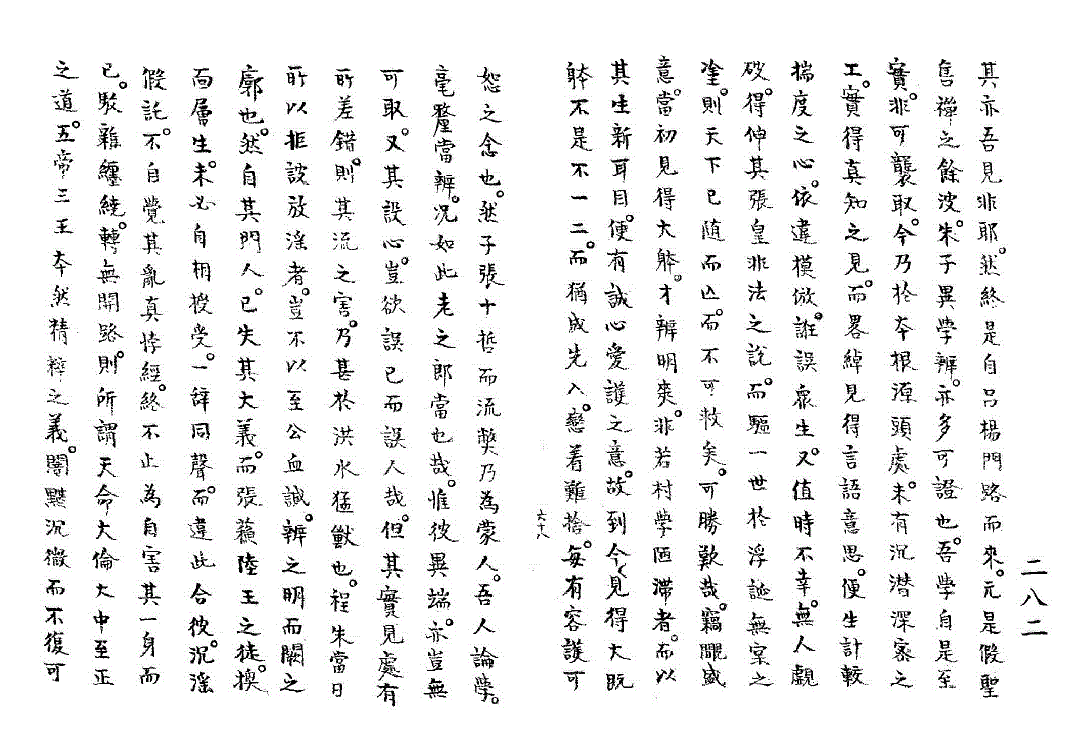 其亦吾见非耶。然终是自吕杨门路而来。元是假圣售禅之馀波。朱子异学辨。亦多可證也。吾学自是至实。非可袭取。今乃于本根源头处。未有沉潜深密之工。实得真知之见。而略绰见得言语意思。便生计较揣度之心。依违模仿。诳误众生。又值时不幸。无人觑破。得伸其张皇非法之说。而驱一世于浮诞无宲之涂。则天下已随而亡。而不可救矣。可胜叹哉。窃覸盛意。当初见得大体。才辨明爽。非若村学陋滞者。而以其生新耳目。便有诚心爱护之意。故到今既见得大体不是不一二。而犹成先入。恋着难舍。每有容护可恕之念也。然子张十哲而流弊乃为蒙人。吾人论学。毫釐当辨。况如此老之郎当也哉。惟彼异端。亦岂无可取。又其设心。岂欲误己而误人哉。但其实见处有所差错。则其流之害。乃甚于洪水猛兽也。程朱当日所以拒诐放淫者。岂不以至公血诚。辨之明而阙之廓也。然自其门人。已失其大义。而张苏陆王之徒。换面层生。未必自相授受。一辞同声。而违此合彼。沉淫假托。不自觉其乱真悖经。终不止为自害其一身而已。驳杂缠绕。转无开路。则所谓天命大伦大中至正之道。五帝三王本然精粹之义。闇黮沈微而不复可
其亦吾见非耶。然终是自吕杨门路而来。元是假圣售禅之馀波。朱子异学辨。亦多可證也。吾学自是至实。非可袭取。今乃于本根源头处。未有沉潜深密之工。实得真知之见。而略绰见得言语意思。便生计较揣度之心。依违模仿。诳误众生。又值时不幸。无人觑破。得伸其张皇非法之说。而驱一世于浮诞无宲之涂。则天下已随而亡。而不可救矣。可胜叹哉。窃覸盛意。当初见得大体。才辨明爽。非若村学陋滞者。而以其生新耳目。便有诚心爱护之意。故到今既见得大体不是不一二。而犹成先入。恋着难舍。每有容护可恕之念也。然子张十哲而流弊乃为蒙人。吾人论学。毫釐当辨。况如此老之郎当也哉。惟彼异端。亦岂无可取。又其设心。岂欲误己而误人哉。但其实见处有所差错。则其流之害。乃甚于洪水猛兽也。程朱当日所以拒诐放淫者。岂不以至公血诚。辨之明而阙之廓也。然自其门人。已失其大义。而张苏陆王之徒。换面层生。未必自相授受。一辞同声。而违此合彼。沉淫假托。不自觉其乱真悖经。终不止为自害其一身而已。驳杂缠绕。转无开路。则所谓天命大伦大中至正之道。五帝三王本然精粹之义。闇黮沈微而不复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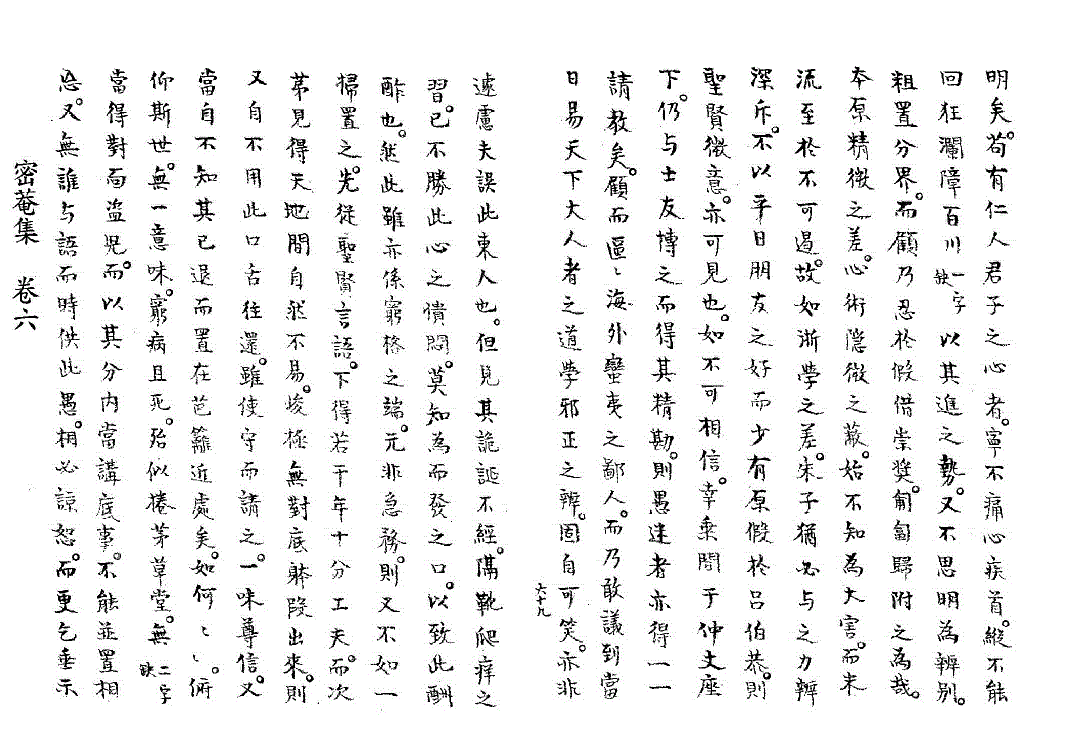 明矣。苟有仁人君子之心者。宁不痛心疾首。纵不能回狂澜障百川(一字缺)以其进之势。又不思明为辨别。粗置分界。而顾乃忍于假借崇奖。匍匐归附之为哉。本原精微之差。心术隐微之蔽。始不知为大害。而末流至于不可遏。故如浙学之差。朱子犹必与之力辨深斥。不以平日朋友之好而少有原假于吕伯恭。则圣贤微意。亦可见也。如不可相信。幸乘间于仲丈座下。仍与士友博之而得其精勘。则愚迷者亦得一一请教矣。顾而区区海外蛮夷之鄙人。而乃敢议到当日易天下大人者之道学邪正之辨。固自可笑。亦非遽虑夫误此东人也。但见其诡诞不经。隔靴爬痒之习。已不胜此心之愦闷。莫知为而发之口。以致此酬酢也。然此虽亦系穷格之端。元非急务。则又不如一扫置之。先从圣贤言语。不得若干年十分工夫。而次第见得天地间自然不易。峻极无对底体段出来。则又自不用此口舌往还。虽使守而请之。一味尊信。又当自不知其已退而置在芭篱近处矣。如何如何。俯仰斯世。无一意味。穷病且死。殆似捲茅莫堂。无(二字缺)当得对面盗儿。而以其分内当讲底事。不能并置相忘。又无谁与语而时供此愚。相必谅恕。而更乞垂示
明矣。苟有仁人君子之心者。宁不痛心疾首。纵不能回狂澜障百川(一字缺)以其进之势。又不思明为辨别。粗置分界。而顾乃忍于假借崇奖。匍匐归附之为哉。本原精微之差。心术隐微之蔽。始不知为大害。而末流至于不可遏。故如浙学之差。朱子犹必与之力辨深斥。不以平日朋友之好而少有原假于吕伯恭。则圣贤微意。亦可见也。如不可相信。幸乘间于仲丈座下。仍与士友博之而得其精勘。则愚迷者亦得一一请教矣。顾而区区海外蛮夷之鄙人。而乃敢议到当日易天下大人者之道学邪正之辨。固自可笑。亦非遽虑夫误此东人也。但见其诡诞不经。隔靴爬痒之习。已不胜此心之愦闷。莫知为而发之口。以致此酬酢也。然此虽亦系穷格之端。元非急务。则又不如一扫置之。先从圣贤言语。不得若干年十分工夫。而次第见得天地间自然不易。峻极无对底体段出来。则又自不用此口舌往还。虽使守而请之。一味尊信。又当自不知其已退而置在芭篱近处矣。如何如何。俯仰斯世。无一意味。穷病且死。殆似捲茅莫堂。无(二字缺)当得对面盗儿。而以其分内当讲底事。不能并置相忘。又无谁与语而时供此愚。相必谅恕。而更乞垂示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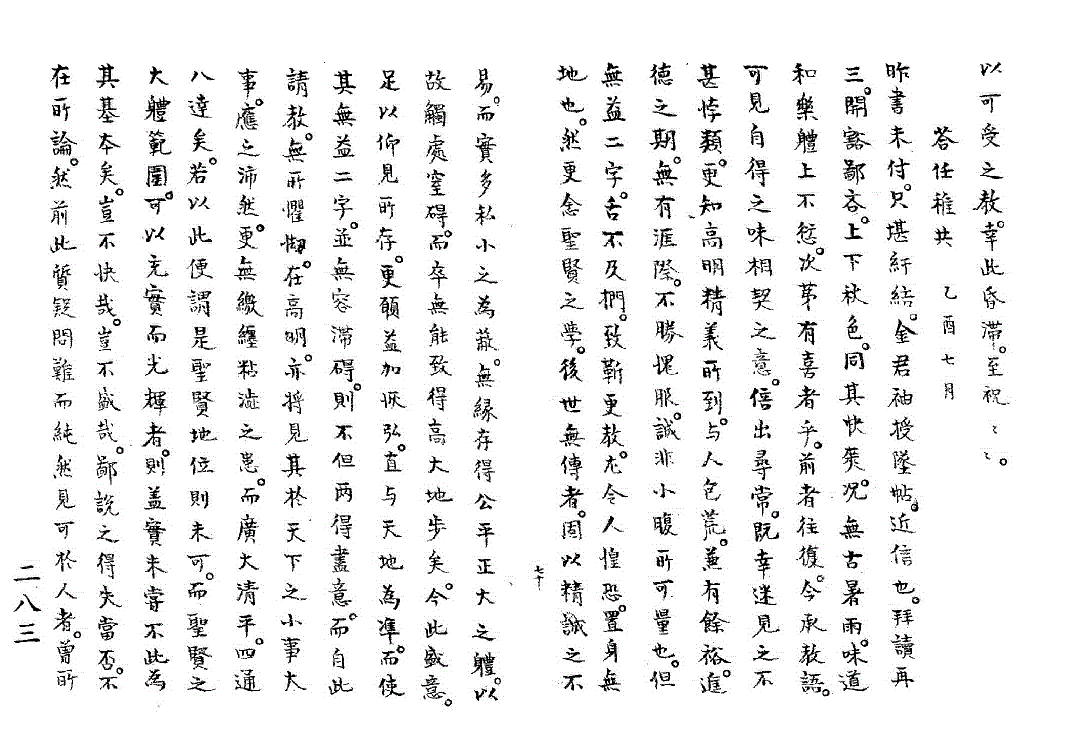 以可受之教。幸此昏滞。至祝至祝。
以可受之教。幸此昏滞。至祝至祝。答任稚共(乙酉七月)
昨书未付。只堪纡结。金君袖授坠帖。近信也。拜读再三。开豁鄙吝。上下秋色。同其快爽。况无古暑雨。味道和乐体上不愆。次第有喜者乎。前者往复。今承教语。可见自得之味相契之意。倍出寻常。既幸迷见之不甚悖类。更知高明精义所到。与人包荒。兼有馀裕。进德之期。无有涯际。不胜愧服。诚非小腹所可量也。但无益二字。舌不及扪。致靳更教。尤令人惶恐。置身无地也。然更念圣贤之学。后世无传者。固以精诚之不易。而实多私小之为蔽。无缘存得公平正大之体。以故触处窒碍。而卒无能致得高大地步矣。今此盛意。足以仰见所存。更愿益加恢弘。直与天地为准。而使其无益二字。并无容滞碍。则不但两得尽意。而自此请教。无所惧㥘。在高明。亦将见其于天下之小事大事。应之沛然。更无缴缠粘涩之患。而广大清平。四通八达矣。若以此便谓是圣贤地位则未可。而圣贤之大体范围。可以充实而光辉者。则盖实未尝不此为其基本矣。岂不快哉。岂不盛哉。鄙说之得失当否。不在所论。然前此质疑问难而纯然见可于人者。曾所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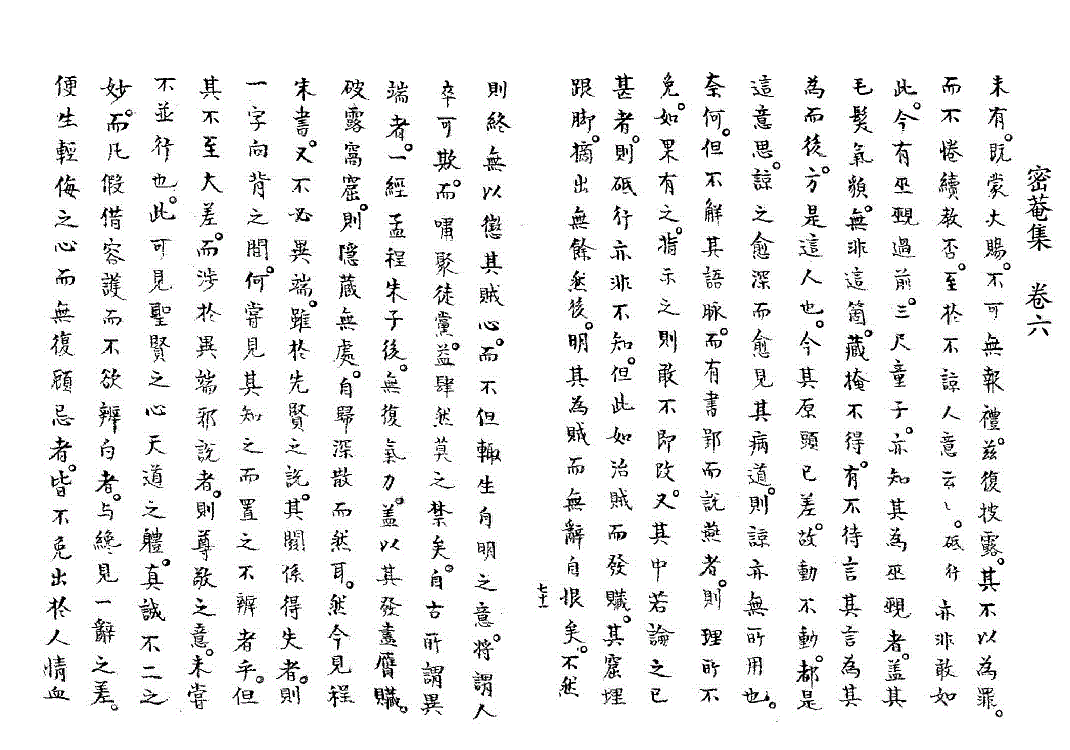 未有。既蒙大赐。不可无报礼。玆复披露。其不以为罪。而不惓续教否。至于不谅人意云云。(砥行)亦非敢如此。今有巫觋过前。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巫觋者。盖其毛发气貌。无非这个。藏掩不得。有不待言其言为其为而后。方是这人也。今其原头已差。故动不动。都是这意思。谅之愈深而愈见其病道。则谅亦无所用也。奈何。但不解其语脉。而有书郢而说燕者。则理所不免。如果有之。指示之则敢不即改。又其中若论之已甚者。则砥行亦非不知。但此如治贼而发赃。其窟埋跟脚。摘出无馀然后。明其为贼而无辞自恨矣。不然则终无以惩其贼心。而不但辄生自明之意。将谓人卒可欺。而啸聚徒党。益肆然莫之禁矣。自古所谓异端者。一经孟程朱子后。无复气力。盖以其发尽赝赃。破露窝窟。则隐藏无处。自归深散而然耳。然今见程朱书。又不必异端。虽于先贤之说。其关系得失者。则一字向背之间。何尝见其知之而置之不辨者乎。但其不至大差。而涉于异端邪说者。则尊敬之意。未尝不并行也。此可见圣贤之心天道之体。真诚不二之妙。而凡假借容护而不欲辨白者。与才见一辞之差。便生轻侮之心而无复顾忌者。皆不免出于人情血
未有。既蒙大赐。不可无报礼。玆复披露。其不以为罪。而不惓续教否。至于不谅人意云云。(砥行)亦非敢如此。今有巫觋过前。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巫觋者。盖其毛发气貌。无非这个。藏掩不得。有不待言其言为其为而后。方是这人也。今其原头已差。故动不动。都是这意思。谅之愈深而愈见其病道。则谅亦无所用也。奈何。但不解其语脉。而有书郢而说燕者。则理所不免。如果有之。指示之则敢不即改。又其中若论之已甚者。则砥行亦非不知。但此如治贼而发赃。其窟埋跟脚。摘出无馀然后。明其为贼而无辞自恨矣。不然则终无以惩其贼心。而不但辄生自明之意。将谓人卒可欺。而啸聚徒党。益肆然莫之禁矣。自古所谓异端者。一经孟程朱子后。无复气力。盖以其发尽赝赃。破露窝窟。则隐藏无处。自归深散而然耳。然今见程朱书。又不必异端。虽于先贤之说。其关系得失者。则一字向背之间。何尝见其知之而置之不辨者乎。但其不至大差。而涉于异端邪说者。则尊敬之意。未尝不并行也。此可见圣贤之心天道之体。真诚不二之妙。而凡假借容护而不欲辨白者。与才见一辞之差。便生轻侮之心而无复顾忌者。皆不免出于人情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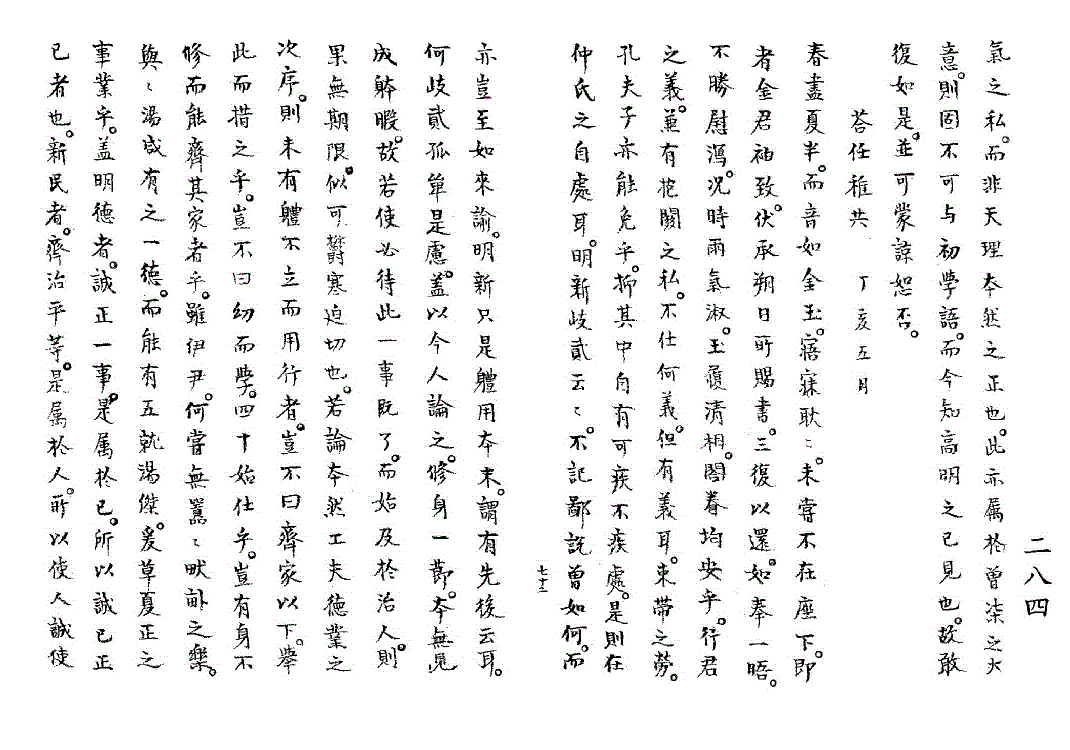 气之私。而非天理本然之正也。此亦属于曾柒之大意。则固不可与初学语。而今知高明之已见也。故敢复如是。并可蒙谅恕否。
气之私。而非天理本然之正也。此亦属于曾柒之大意。则固不可与初学语。而今知高明之已见也。故敢复如是。并可蒙谅恕否。答任稚共(丁亥五月)
春尽夏半。而音如金玉。寤寐耿耿。未尝不在座下。即者金君袖致。伏承朔日所赐书。三复以还。如奉一晤。不胜慰泻。况时雨气淑。玉履清相。閤眷均安乎。行君之义。兼有抱关之私。不仕何义。但有义耳。束带之劳。孔夫子亦能免乎。抑其中自有可疾不疾处。是则在仲氏之自处耳。明新岐贰云云。不记鄙说曾如何。而亦岂至如来谕。明新只是体用本末。谓有先后云耳。何岐贰孤单是虑。盖以今人论之。修身一节。本无见成体暇。故若使必待此一事既了。而始及于治人。则果无期限。似可郁寒迫切也。若论本然工夫德业之次序。则未有体不立而用行者。岂不曰齐家以下。举此而措之乎。岂不曰幼而学。四十始仕乎。岂有身不修而能齐其家者乎。虽伊尹。何尝无嚣嚣畎亩之乐。与与汤咸有之一德。而能有五就汤杰。爰草夏正之事业乎。盖明德者。诚正一事。是属于己。所以诚己正己者也。新民者。齐治平等。是属于人。所以使人诚使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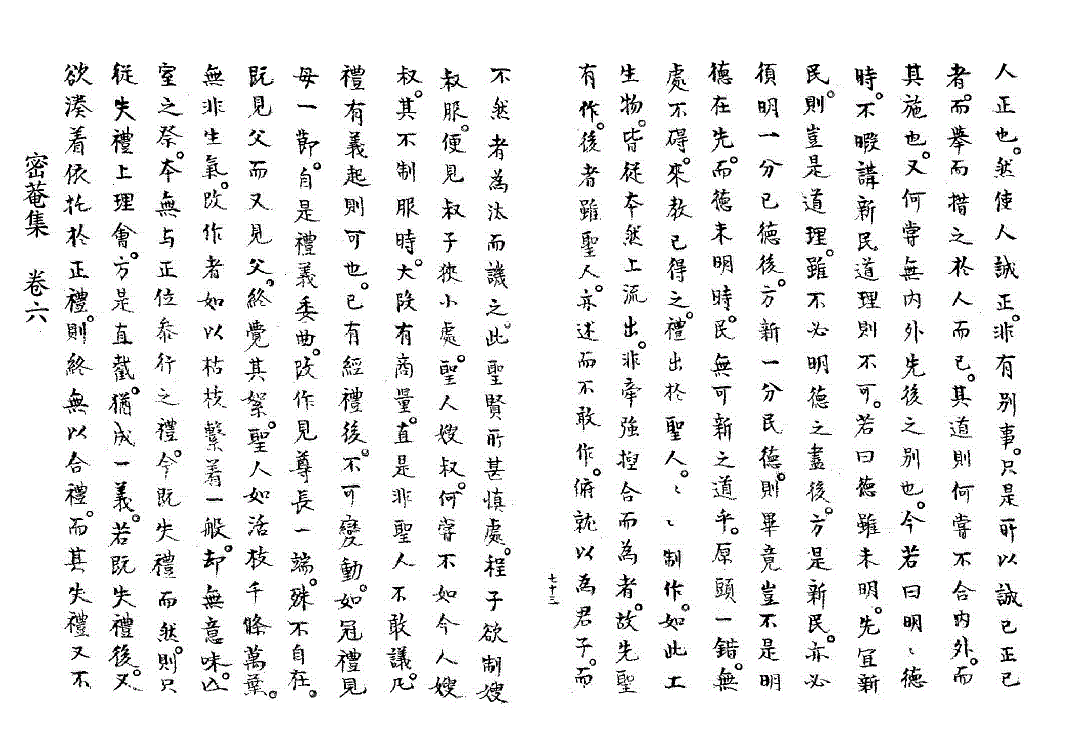 人正也。然使人诚正。非有别事。只是所以诚己正己者。而举而措之于人而已。其道则何尝不合内外。而其施也。又何尝无内外先后之别也。今若曰明明德时。不暇讲新民道理则不可。若曰德虽未明。先宜新民。则岂是道理。虽不必明德之尽后。方是新民。亦必须明一分己德后。方新一分民德。则毕竟岂不是明德在先。而德未明时。民无可新之道乎。原头一错。无处不碍。来教已得之。礼出于圣人。圣人制作。如此工生物。皆从本然上流出。非牵强捏合而为者。故先圣有作。后者虽圣人。亦述而不敢作。俯就以为君子。而不然者为汰而讥之。此圣贤所甚慎处。程子欲制嫂叔服。便见叔子狭小处。圣人嫂叔。何尝不如今人嫂叔。其不制服时。大段有商量。直是非圣人不敢议。凡礼有义起则可也。已有经礼后。不可变动。如冠礼见母一节。自是礼义委曲。改作见尊长一端。殊不自在。既见父而又见父。终觉其絮。圣人如活枝千条万叶。无非生气。改作者如以枯枝系着一般。却无意味。亡室之祭。本无与正位参行之礼。今既失礼而然。则只从失礼上理会。方是直截。犹成一义。若既失礼后。又欲凑着依托于正礼。则终无以合礼。而其失礼又不
人正也。然使人诚正。非有别事。只是所以诚己正己者。而举而措之于人而已。其道则何尝不合内外。而其施也。又何尝无内外先后之别也。今若曰明明德时。不暇讲新民道理则不可。若曰德虽未明。先宜新民。则岂是道理。虽不必明德之尽后。方是新民。亦必须明一分己德后。方新一分民德。则毕竟岂不是明德在先。而德未明时。民无可新之道乎。原头一错。无处不碍。来教已得之。礼出于圣人。圣人制作。如此工生物。皆从本然上流出。非牵强捏合而为者。故先圣有作。后者虽圣人。亦述而不敢作。俯就以为君子。而不然者为汰而讥之。此圣贤所甚慎处。程子欲制嫂叔服。便见叔子狭小处。圣人嫂叔。何尝不如今人嫂叔。其不制服时。大段有商量。直是非圣人不敢议。凡礼有义起则可也。已有经礼后。不可变动。如冠礼见母一节。自是礼义委曲。改作见尊长一端。殊不自在。既见父而又见父。终觉其絮。圣人如活枝千条万叶。无非生气。改作者如以枯枝系着一般。却无意味。亡室之祭。本无与正位参行之礼。今既失礼而然。则只从失礼上理会。方是直截。犹成一义。若既失礼后。又欲凑着依托于正礼。则终无以合礼。而其失礼又不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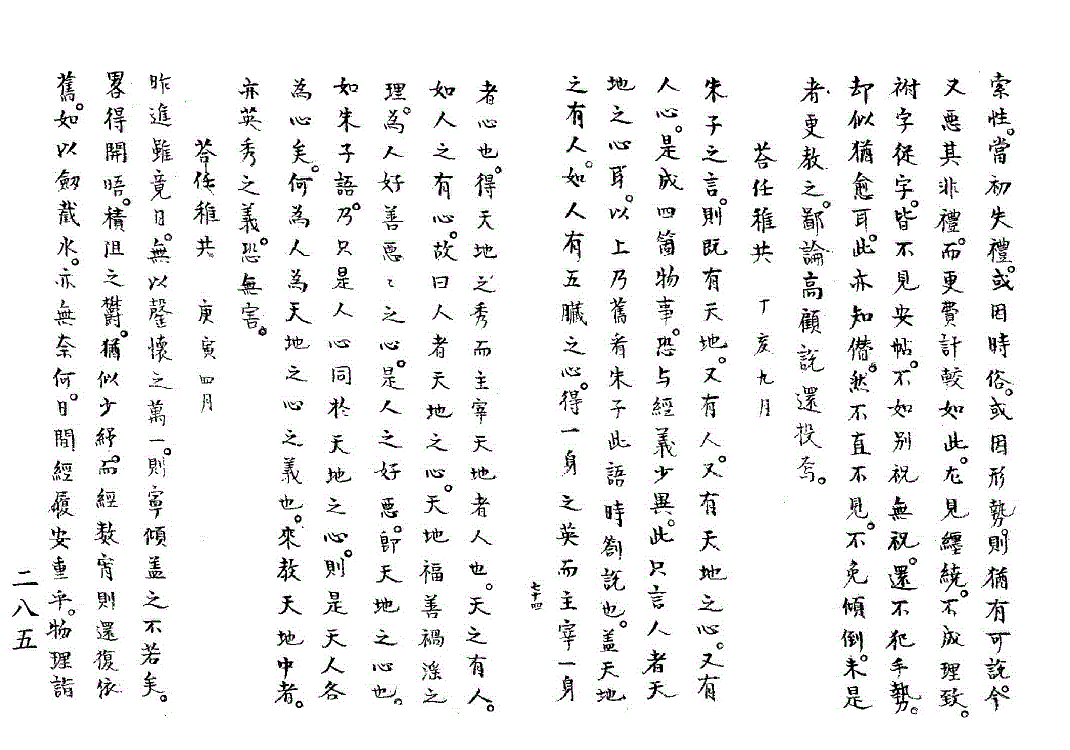 索性。当初失礼。或因时俗。或因形势。则犹有可说。今又恶其非礼。而更费计较如此。尤见缠绕。不成理致。祔字从字。皆不见安帖。不如别祝无祝。还不犯手势。却似犹愈耳。此亦知僭。然不直不见。不免倾倒。未是者更教之。鄙论高顾说还投焉。
索性。当初失礼。或因时俗。或因形势。则犹有可说。今又恶其非礼。而更费计较如此。尤见缠绕。不成理致。祔字从字。皆不见安帖。不如别祝无祝。还不犯手势。却似犹愈耳。此亦知僭。然不直不见。不免倾倒。未是者更教之。鄙论高顾说还投焉。答任稚共(丁亥九月)
朱子之言。则既有天地。又有人。又有天地之心。又有人心。是成四个物事。恐与经义少异。此只言人者天地之心耳。以上乃旧看朱子此语时劄说也。盖天地之有人。如人有五脏之心。得一身之英而主宰一身者心也。得天地之秀而主宰天地者人也。天之有人。如人之有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天地福善祸淫之理。为人好善恶恶之心。是人之好恶。即天地之心也。如朱子语。乃只是人心同于天地之心。则是天人各为心矣。何为人为天地之心之义也。来教天地中者。亦英秀之义。恐无害。
答任稚共(庚寅四月)
昨进虽竟日。无以罄怀之万一。则宁倾盖之不若矣。略得开晤。积阻之郁。犹似少纾。而经数宵则还复依旧。如以剑截水。亦无奈何。日间经履安重乎。物理诣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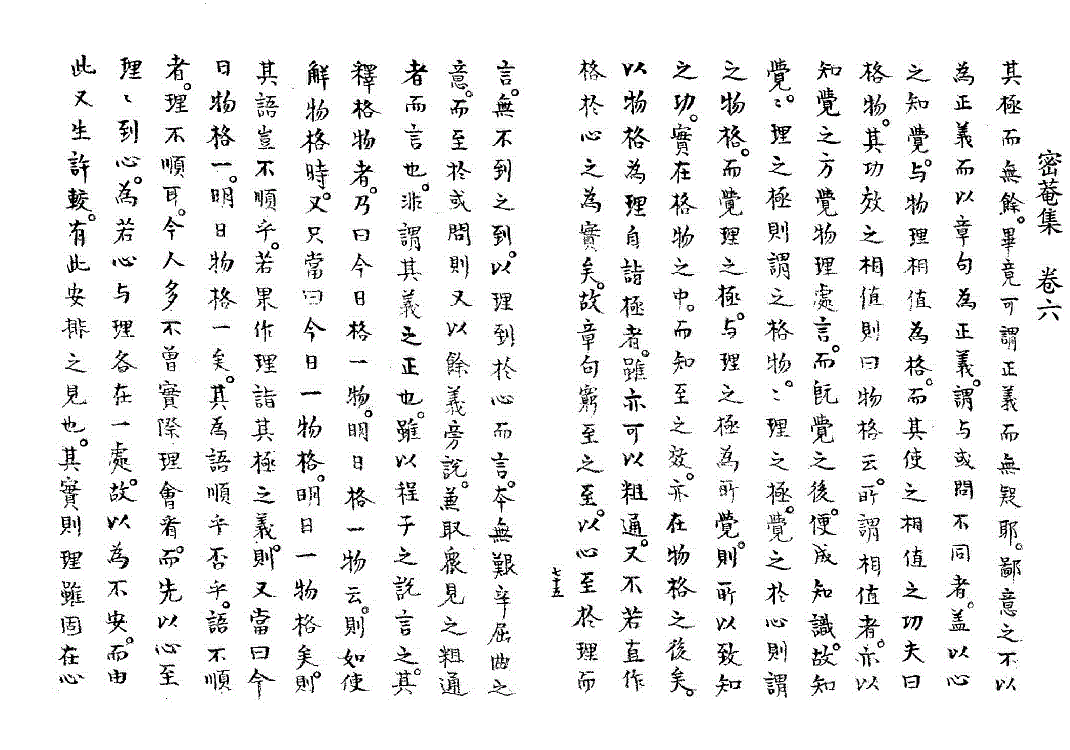 其极而无馀。毕竟可谓正义而无疑耶。鄙意之不以为正义而以章句为正义。谓与或问不同者。盖以心之知觉。与物理相值为格。而其使之相值之功夫曰格物。其功效之相值则曰物格云。所谓相值者。亦以知觉之方觉物理处言。而既觉之后。便成知识。故知觉。觉理之极则谓之格物。物理之极。觉之于心则谓之物格。而觉理之极。与理之极为所觉。则所以致知之功。实在格物之中。而知至之效。亦在物格之后矣。以物格为理自诣极者。虽亦可以粗通。又不若直作格于心之为实矣。故章句穷至之至。以心至于理而言。无不到之到。以理到于心而言。本无艰辛屈曲之意。而至于或问则又以馀义旁说。兼取众见之粗通者而言也。非谓其义之正也。虽以程子之说言之。其释格物者。乃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则如使解物格时。又只当曰今日一物格。明日一物格矣。则其语岂不顺乎。若果作理诣其极之义。则又当曰今日物格一。明日物格一矣。其为语顺乎否乎。语不顺者。理不顺耳。今人多不曾实际理会看。而先以心至理理到心。为若心与理各在一处。故以为不安。而由此又生许较。有此安排之见也。其实则理虽固在心
其极而无馀。毕竟可谓正义而无疑耶。鄙意之不以为正义而以章句为正义。谓与或问不同者。盖以心之知觉。与物理相值为格。而其使之相值之功夫曰格物。其功效之相值则曰物格云。所谓相值者。亦以知觉之方觉物理处言。而既觉之后。便成知识。故知觉。觉理之极则谓之格物。物理之极。觉之于心则谓之物格。而觉理之极。与理之极为所觉。则所以致知之功。实在格物之中。而知至之效。亦在物格之后矣。以物格为理自诣极者。虽亦可以粗通。又不若直作格于心之为实矣。故章句穷至之至。以心至于理而言。无不到之到。以理到于心而言。本无艰辛屈曲之意。而至于或问则又以馀义旁说。兼取众见之粗通者而言也。非谓其义之正也。虽以程子之说言之。其释格物者。乃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则如使解物格时。又只当曰今日一物格。明日一物格矣。则其语岂不顺乎。若果作理诣其极之义。则又当曰今日物格一。明日物格一矣。其为语顺乎否乎。语不顺者。理不顺耳。今人多不曾实际理会看。而先以心至理理到心。为若心与理各在一处。故以为不安。而由此又生许较。有此安排之见也。其实则理虽固在心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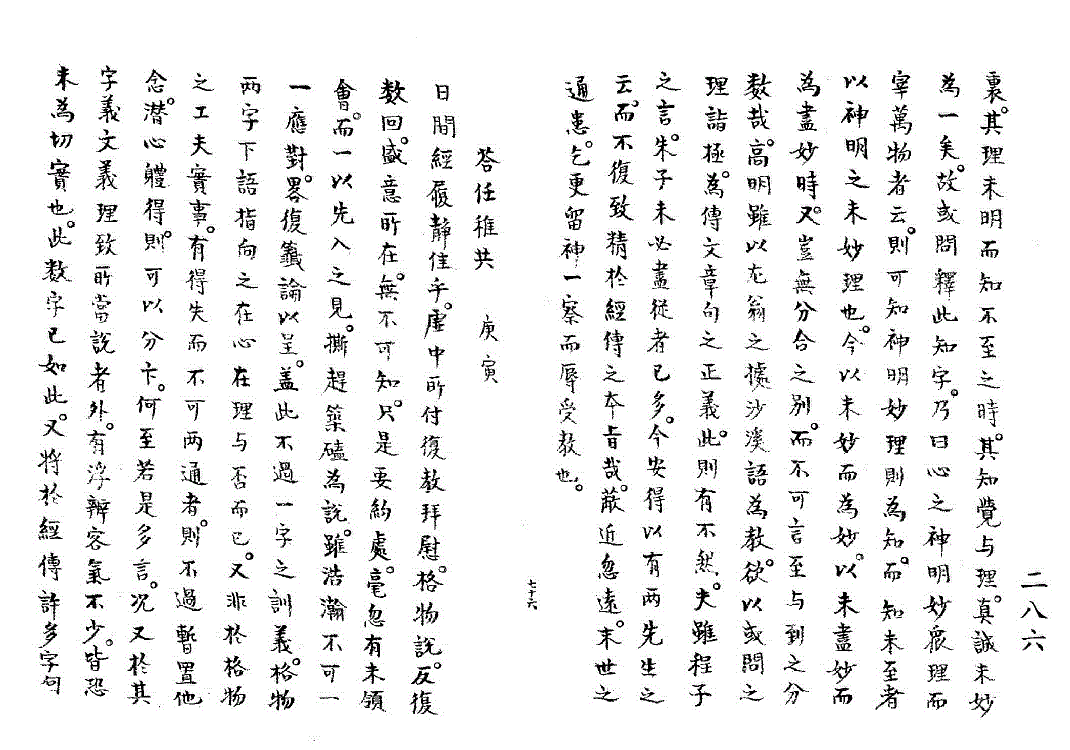 里。其理未明而知不至之时。其知觉与理。真诚未妙为一矣。故或问释此知字。乃曰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云。则可知神明妙理则为知。而知未至者以神明之未妙理也。今以未妙而为妙。以未尽妙而为尽妙时。又岂无分合之别。而不可言至与到之分数哉。高明虽以尤翁之据沙溪语为教。欲以或问之理诣极。为传文章句之正义。此则有不然。夫虽程子之言。朱子未必尽从者已多。今安得以有两先生之云。而不复致精于经传之本旨哉。蔽近忽远。末世之通患。乞更留神一察而辱受教也。
里。其理未明而知不至之时。其知觉与理。真诚未妙为一矣。故或问释此知字。乃曰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云。则可知神明妙理则为知。而知未至者以神明之未妙理也。今以未妙而为妙。以未尽妙而为尽妙时。又岂无分合之别。而不可言至与到之分数哉。高明虽以尤翁之据沙溪语为教。欲以或问之理诣极。为传文章句之正义。此则有不然。夫虽程子之言。朱子未必尽从者已多。今安得以有两先生之云。而不复致精于经传之本旨哉。蔽近忽远。末世之通患。乞更留神一察而辱受教也。答任稚共(庚寅)
日间经履静佳乎。虚中所付复教拜慰。格物说。反复数回。盛意所在。无不可知。只是要约处。毫忽有未领会。而一以先入之见。撕赶筑磕为说。虽浩瀚不可一一应对。略复签论以呈。盖此不过一字之训义。格物两字下语指向之在心在理与否而已。又非于格物之工夫实事。有得失而不可两通者。则不过暂置他念。潜心体得。则可以分卞。何至若是多言。况又于其字义文义理致所当说者外。有浮辨客气不少。皆恐未为切实也。此数字已如此。又将于经传许多字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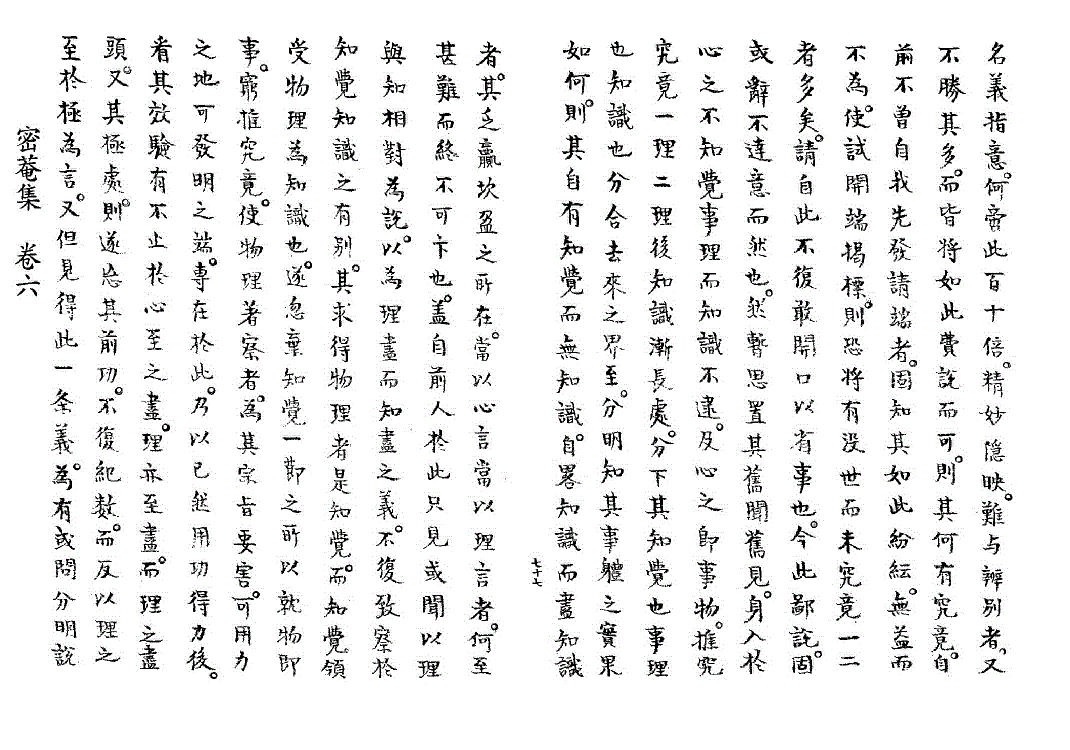 名义指意。何啻此百十倍。精妙隐映。难与辨别者。又不胜其多。而皆将如此费说而可。则其何有究竟。自前不曾自我先发请端者。固知其如此纷纭。无益而不为。使试开端揭标。则恐将有没世而未究竟一二者多矣。请自此不复敢开口以省事也。今此鄙说。固或辞不达意而然也。然暂思置其旧闻旧见。身入于心之不知觉事理而知识不逮。及心之即事物。推究究竟一理二理后知识渐长处。分下其知觉也事理也知识也分合去来之界至。分明知其事体之实果如何。则其自有知觉而无知识。自略知识而尽知识者。其乏赢坎盈之所在。当以心言当以理言者。何至甚难而终不可卞也。盖自前人于此只见或闻以理与知相对为说。以为理尽而知尽之义。不复致察于知觉知识之有别。其求得物理者是知觉。而知觉领受物理为知识也。遂忽弃知觉一节之所以就物即事。穷推究竟。使物理著察者。为其宗旨要害。可用力之地可发明之端。专在于此。乃以已然用功得力后。看其效验有不止于心至之尽。理亦至尽。而理之尽头。又其极处。则遂忘其前功。不复纪数。而反以理之至于极为言。又但见得此一条义。为有或问分明说
名义指意。何啻此百十倍。精妙隐映。难与辨别者。又不胜其多。而皆将如此费说而可。则其何有究竟。自前不曾自我先发请端者。固知其如此纷纭。无益而不为。使试开端揭标。则恐将有没世而未究竟一二者多矣。请自此不复敢开口以省事也。今此鄙说。固或辞不达意而然也。然暂思置其旧闻旧见。身入于心之不知觉事理而知识不逮。及心之即事物。推究究竟一理二理后知识渐长处。分下其知觉也事理也知识也分合去来之界至。分明知其事体之实果如何。则其自有知觉而无知识。自略知识而尽知识者。其乏赢坎盈之所在。当以心言当以理言者。何至甚难而终不可卞也。盖自前人于此只见或闻以理与知相对为说。以为理尽而知尽之义。不复致察于知觉知识之有别。其求得物理者是知觉。而知觉领受物理为知识也。遂忽弃知觉一节之所以就物即事。穷推究竟。使物理著察者。为其宗旨要害。可用力之地可发明之端。专在于此。乃以已然用功得力后。看其效验有不止于心至之尽。理亦至尽。而理之尽头。又其极处。则遂忘其前功。不复纪数。而反以理之至于极为言。又但见得此一条义。为有或问分明说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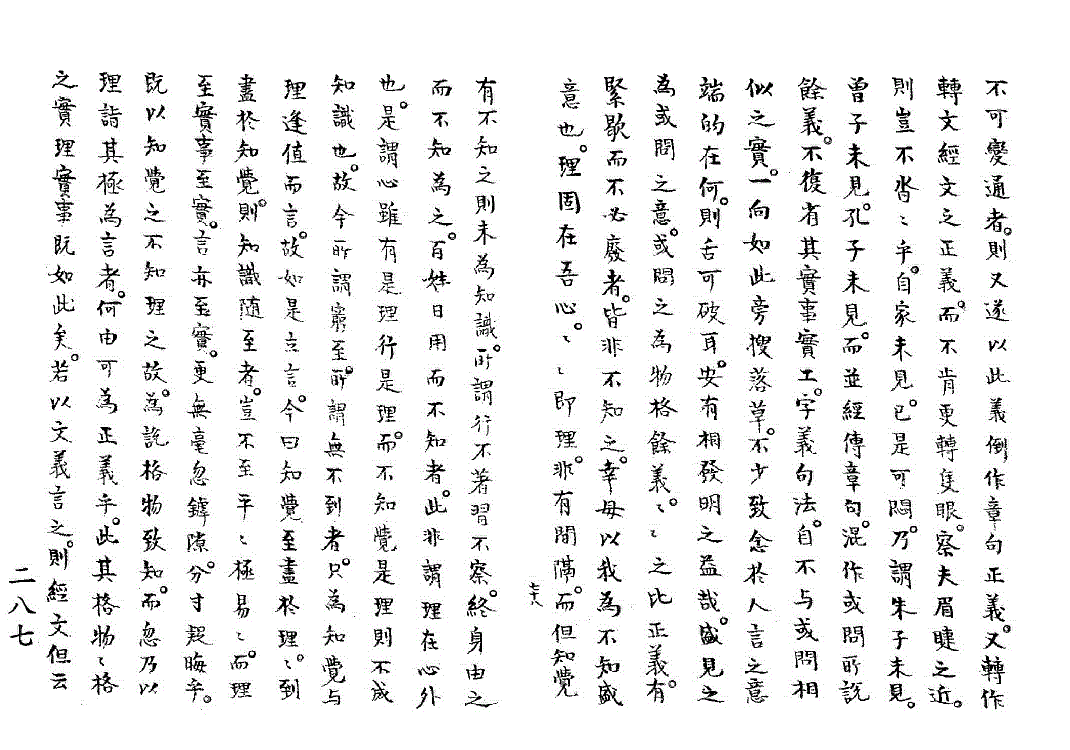 不可变通者。则又遂以此义倒作章句正义。又转作转文经文之正义。而不肯更转只眼。察夫眉睫之近。则岂不沓沓乎。自家未见。已是可闷。乃谓朱子未见。曾子未见。孔子未见。而并经传章句。混作或问所说馀义。不复省其实事实工。字义句法。自不与或问相似之实。一向如此旁搜落草。不少致念于人言之意端的在何。则舌可破耳。安有相发明之益哉。盛见之为或问之意。或问之为物格馀义。馀义之比正义。有紧歇而不必废者。皆非不知之。幸毋以我为不知盛意也。理固在吾心。吾心即理。非有间隔。而但知觉有不知之则未为知识。所谓行不著习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为之。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非谓理在心外也。是谓心虽有是理行是理。而不知觉是理则不成知识也。故今所谓穷至。所谓无不到者。只为知觉与理逢值而言。故如是立言。今曰知觉至尽于理。理到尽于知觉。则知识随至者。岂不至平平极易易。而理至实事至实。言亦至实。更无毫忽鏬隙。分寸疑晦乎。既以知觉之不知理之故。为说格物致知。而忽乃以理诣其极为言者。何由可为正义乎。此其格物物格之实理实事既如此矣。若以文义言之。则经文但云
不可变通者。则又遂以此义倒作章句正义。又转作转文经文之正义。而不肯更转只眼。察夫眉睫之近。则岂不沓沓乎。自家未见。已是可闷。乃谓朱子未见。曾子未见。孔子未见。而并经传章句。混作或问所说馀义。不复省其实事实工。字义句法。自不与或问相似之实。一向如此旁搜落草。不少致念于人言之意端的在何。则舌可破耳。安有相发明之益哉。盛见之为或问之意。或问之为物格馀义。馀义之比正义。有紧歇而不必废者。皆非不知之。幸毋以我为不知盛意也。理固在吾心。吾心即理。非有间隔。而但知觉有不知之则未为知识。所谓行不著习不察。终身由之而不知为之。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非谓理在心外也。是谓心虽有是理行是理。而不知觉是理则不成知识也。故今所谓穷至。所谓无不到者。只为知觉与理逢值而言。故如是立言。今曰知觉至尽于理。理到尽于知觉。则知识随至者。岂不至平平极易易。而理至实事至实。言亦至实。更无毫忽鏬隙。分寸疑晦乎。既以知觉之不知理之故。为说格物致知。而忽乃以理诣其极为言者。何由可为正义乎。此其格物物格之实理实事既如此矣。若以文义言之。则经文但云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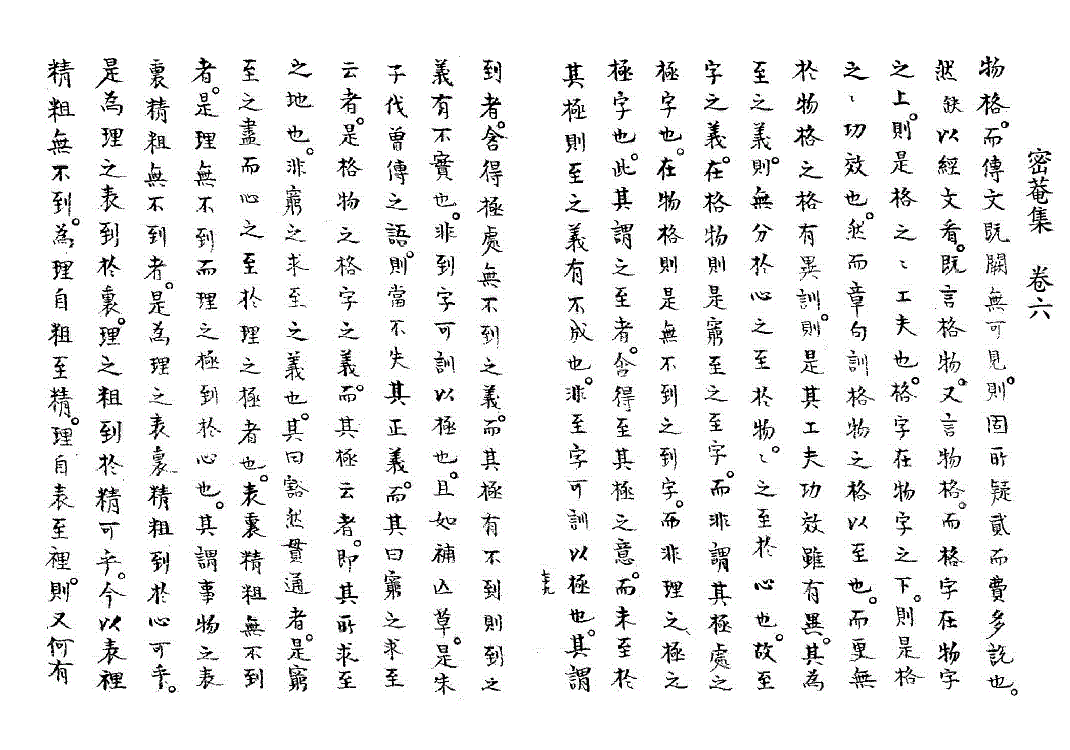 物格。而传文既阙无可见。则固所疑贰而费多说也。然(缺)以经文看。既言格物。又言物格。而格字在物字之上。则是格之之工夫也。格字在物字之下。则是格之之功效也。然而章句训格物之格以至也。而更无于物格之格有异训。则是其工夫功效虽有异。其为至之义。则无分于心之至于物。物之至于心也。故至字之义。在格物则是穷至之至字。而非谓其极处之极字也。在物格则是无不到之到字。而非理之极之极字也。此其谓之至者。含得至其极之意。而未至于其极则至之义有不成也。非至字可训以极也。其谓到者。含得极处无不到之义。而其极有不到则到之义有不实也。非到字可训以极也。且如补亡草。是朱子伐曾传之语。则当不失其正义。而其曰穷之求至云者。是格物之格字之义。而其极云者。即其所求至之地也。非穷之求至之义也。其曰豁然贯通者。是穷至之尽而心之至于理之极者也。表里精粗无不到者。是理无不到而理之极到于心也。其谓事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者。是为理之表里精粗到于心可乎。是为理之表到于里。理之粗到于精可乎。今以表里精粗无不到。为理自粗至精。理自表至里。则又何有
物格。而传文既阙无可见。则固所疑贰而费多说也。然(缺)以经文看。既言格物。又言物格。而格字在物字之上。则是格之之工夫也。格字在物字之下。则是格之之功效也。然而章句训格物之格以至也。而更无于物格之格有异训。则是其工夫功效虽有异。其为至之义。则无分于心之至于物。物之至于心也。故至字之义。在格物则是穷至之至字。而非谓其极处之极字也。在物格则是无不到之到字。而非理之极之极字也。此其谓之至者。含得至其极之意。而未至于其极则至之义有不成也。非至字可训以极也。其谓到者。含得极处无不到之义。而其极有不到则到之义有不实也。非到字可训以极也。且如补亡草。是朱子伐曾传之语。则当不失其正义。而其曰穷之求至云者。是格物之格字之义。而其极云者。即其所求至之地也。非穷之求至之义也。其曰豁然贯通者。是穷至之尽而心之至于理之极者也。表里精粗无不到者。是理无不到而理之极到于心也。其谓事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者。是为理之表里精粗到于心可乎。是为理之表到于里。理之粗到于精可乎。今以表里精粗无不到。为理自粗至精。理自表至里。则又何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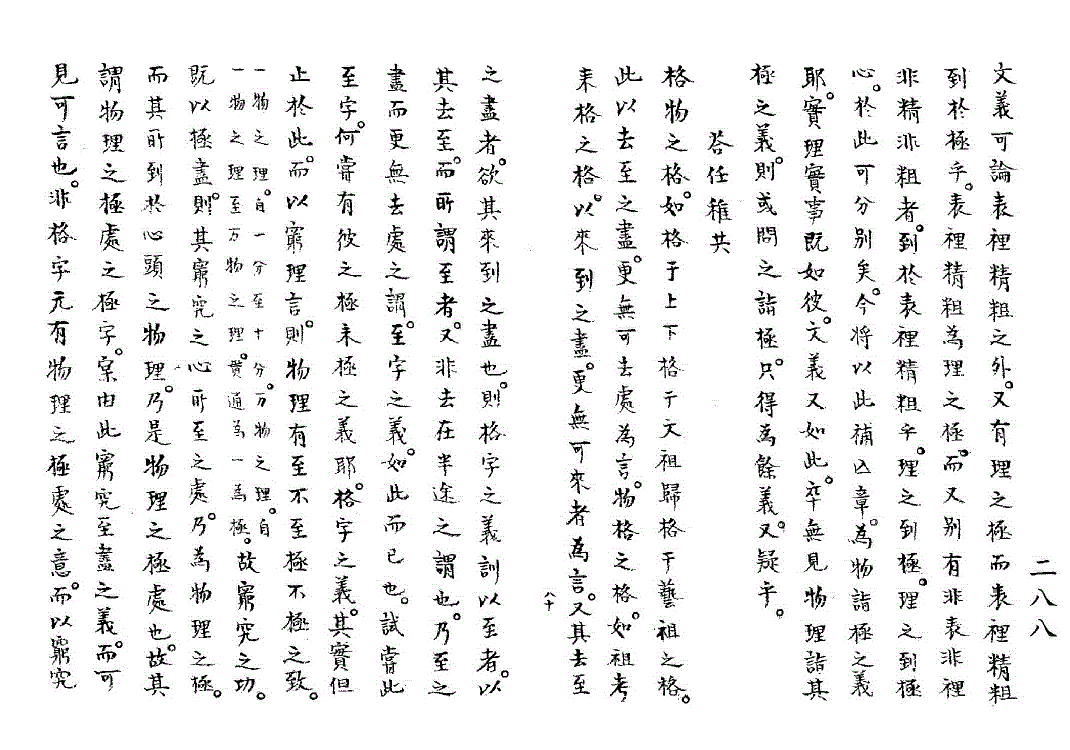 文义可论表里精粗之外。又有理之极而表里精粗到于极乎。表里精粗为理之极。而又别有非表非里非精非粗者。到于表里精粗乎。理之到极。理之到极心。于此可分别矣。今将以此补亡章。为物诣极之义耶。实理实事既如彼。文义又如此。卒无见物理诣其极之义。则或问之诣极。只得为馀义。又疑乎。
文义可论表里精粗之外。又有理之极而表里精粗到于极乎。表里精粗为理之极。而又别有非表非里非精非粗者。到于表里精粗乎。理之到极。理之到极心。于此可分别矣。今将以此补亡章。为物诣极之义耶。实理实事既如彼。文义又如此。卒无见物理诣其极之义。则或问之诣极。只得为馀义。又疑乎。答任稚共
格物之格。如格于上下格于文祖归格于艺祖之格。此以去至之尽。更无可去处为言。物格之格。如祖考来格之格。以来到之尽。更无可来者为言。又其去至之尽者。欲其来到之尽也。则格字之义训以至者。以其去至。而所谓至者。又非去在半途之谓也。乃至之尽而更无去处之谓。至字之义。如此而已也。试尝此至字。何尝有彼之极未极之义耶。格字之义。其实但止于此。而以穷理言。则物理有至不至极不极之致。(一物之理。自一分至十分。万物之理。自一物之理至万物之理。贯通为一为极。)故穷究之功。既以极尽。则其穷究之心所至之处。乃为物理之极。而其所到于心头之物理。乃是物理之极处也。故其谓物理之极处之极字。宲由此穷究至尽之义。而可见可言也。非格字元有物理之极处之意。而以穷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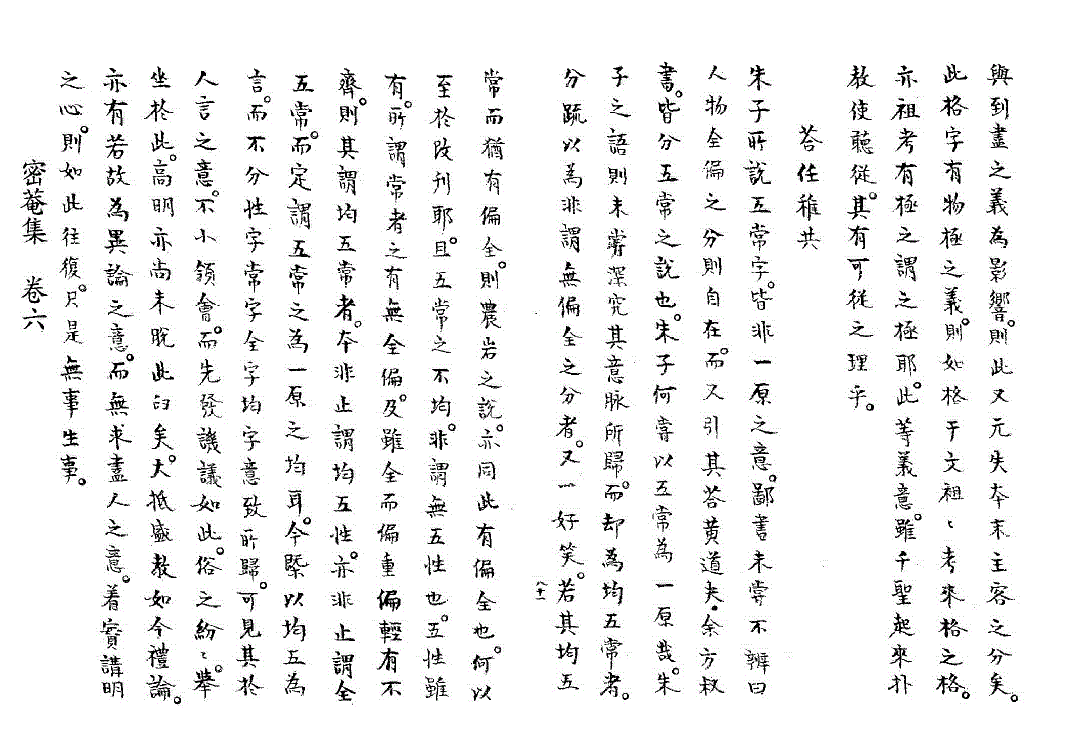 与到尽之义为影响。则此又元失本末主客之分矣。此格字有物极之义。则如格于文祖祖考来格之格。亦祖考有极之谓之极耶。此等义意。虽千圣起来扑教使听从。其有可从之理乎。
与到尽之义为影响。则此又元失本末主客之分矣。此格字有物极之义。则如格于文祖祖考来格之格。亦祖考有极之谓之极耶。此等义意。虽千圣起来扑教使听从。其有可从之理乎。答任稚共
朱子所说五常字。皆非一原之意。鄙书未尝不辨曰人物全偏之分则自在。而又引其答黄道夫,余方叔书。皆分五常之说也。朱子何尝以五常为一原哉。朱子之语则未尝深究其意脉所归。而却为均五常者。分疏以为非谓无偏全之分者。又一好笑。若其均五常而犹有偏全。则农岩之说。亦同此有偏全也。何以至于改刊耶。且五常之不均。非谓无五性也。五性虽有。所谓常者之有无全偏。及虽全而偏重偏轻有不齐。则其谓均五常者。本非止谓均五性。亦非止谓全五常。而定谓五常之为一原之均耳。今槩以均五为言。而不分性字常字全字均字意致所归。可见其于人言之意。不小领会。而先发讥议如此。俗之纷纷。举坐于此。高明亦尚未脱此臼矣。大抵盛教如今礼论。亦有若故为异论之意。而无求尽人之意。着实讲明之心。则如此往复。只是无事生事。
答任稚共
阳明精神气魄。固为千万人之秀。而学术既差。反不如与草木同腐之田夫野老。何足道哉。故于原头未正。则是成焉能为有无者矣。但见才气而他无足观。以吾所见。则其经义亦全没意味。君子不学则已。学则自有圣贤。于此等流涎。将如圣贤何。将如舜何予何何。铁坑零金。不足为贵耳。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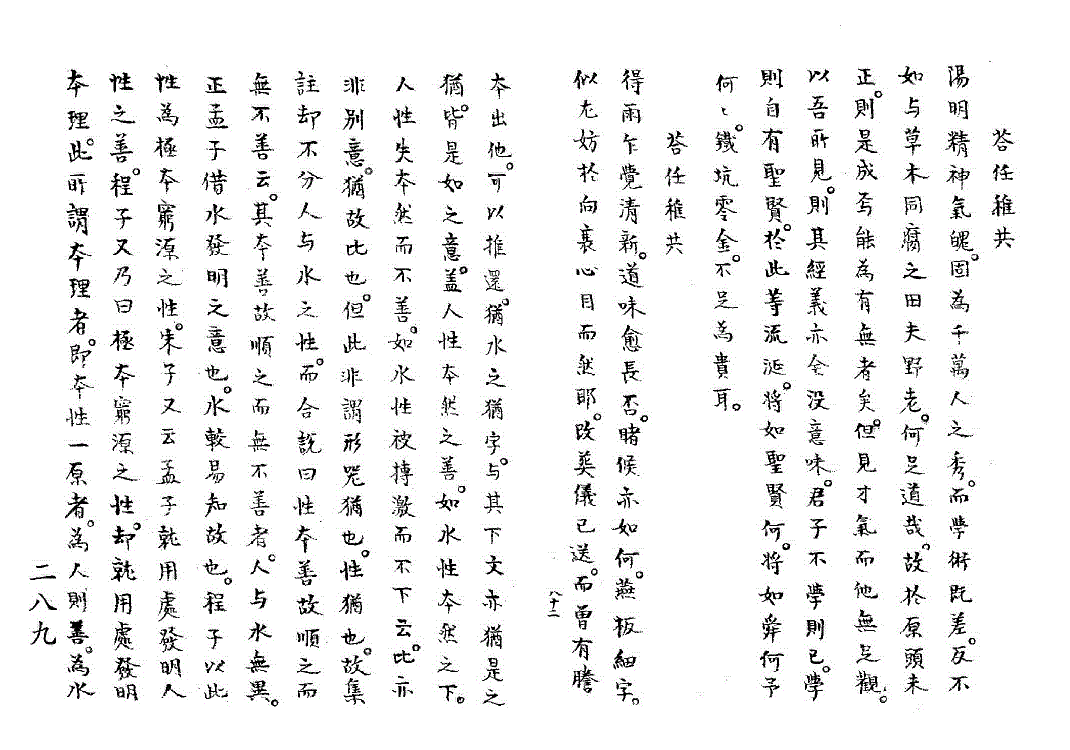 答任稚共
答任稚共得雨乍觉清新。道味愈长否。睹候亦如何。燕板细字。似尤妨于向衰心目而然耶。改葬仪已送。而曾有誊本出他。可以推还。犹水之犹字。与其下文亦犹是之犹。皆是如之意。盖人性本然之善。如水性本然之下。人性失本然而不善。如水性被搏激而不下云。比亦非别意。犹故比也。但此非谓形器犹也。性犹也。故集注却不分人与水之性。而合说曰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云。其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者。人与水无异。正孟子借水发明之意也。水较易知故也。程子以此性为极本穷源之性。朱子又云孟子就用处发明人性之善。程子又乃曰极本穷源之性。却就用处发明本理。此所谓本理者。即本性一原者。为人则善。为水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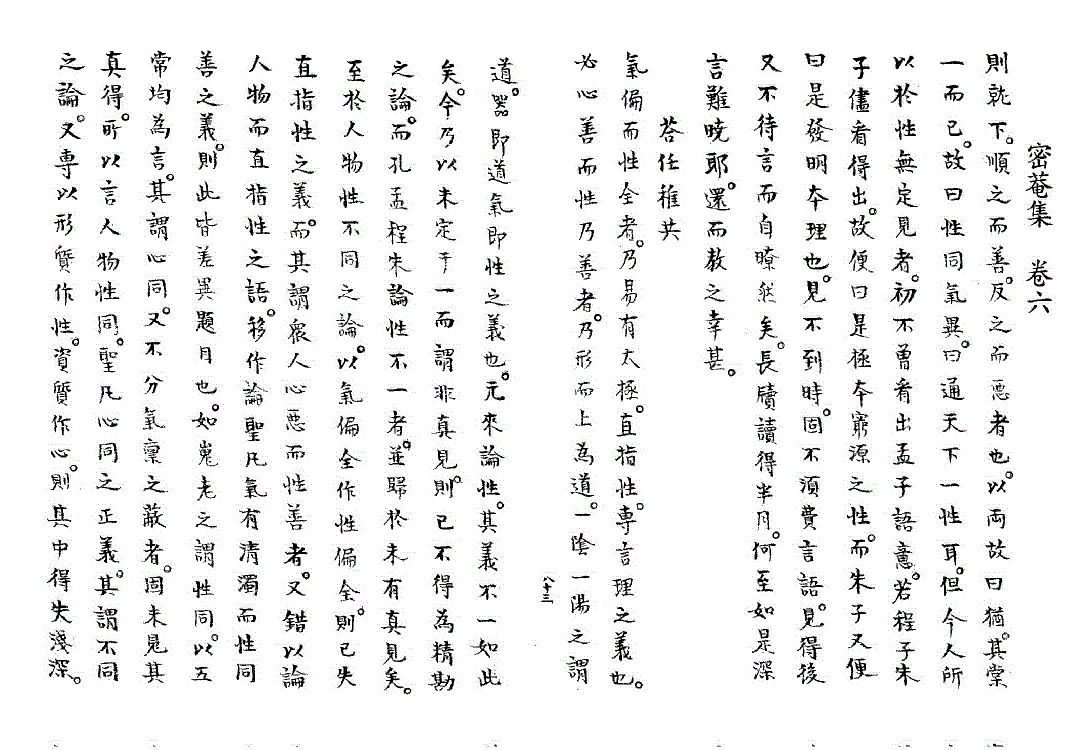 则就下。顺之而善。反之而恶者也。以两故曰犹。其棠一而已。故曰性同气异。曰通天下一性耳。但今人所以于性无定见者。初不曾看出孟子语意。若程子朱子尽看得出。故便曰是极本穷源之性。而朱子又便曰是发明本理也。见不到时。固不须费言语。见得后又不待言而自暸然矣。长牍读得半月。何至如是深言难晓耶。还而教之幸甚。
则就下。顺之而善。反之而恶者也。以两故曰犹。其棠一而已。故曰性同气异。曰通天下一性耳。但今人所以于性无定见者。初不曾看出孟子语意。若程子朱子尽看得出。故便曰是极本穷源之性。而朱子又便曰是发明本理也。见不到时。固不须费言语。见得后又不待言而自暸然矣。长牍读得半月。何至如是深言难晓耶。还而教之幸甚。答任稚共
气偏而性全者。乃易有太极。直指性。专言理之义也。必心善而性乃善者。乃形而上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器即道气即性之义也。元来论性。其义不一如此矣。今乃以未定于一而谓非真见。则已不得为精勘之论。而孔孟程朱论性不一者。并归于未有真见矣。至于人物性不同之论。以气偏全作性偏全。则已失直指性之义。而其谓众人心恶而性善者。又错以论人物而直指性之语。移作论圣凡气有清浊而性同善之义。则此皆差异题目也。如嵬老之谓性同。以五常均为言。其谓心同。又不分气禀之蔽者。固未见其真得。所以言人物性同。圣凡心同之正义。其谓不同之论。又专以形质作性。资质作心。则其中得失浅深。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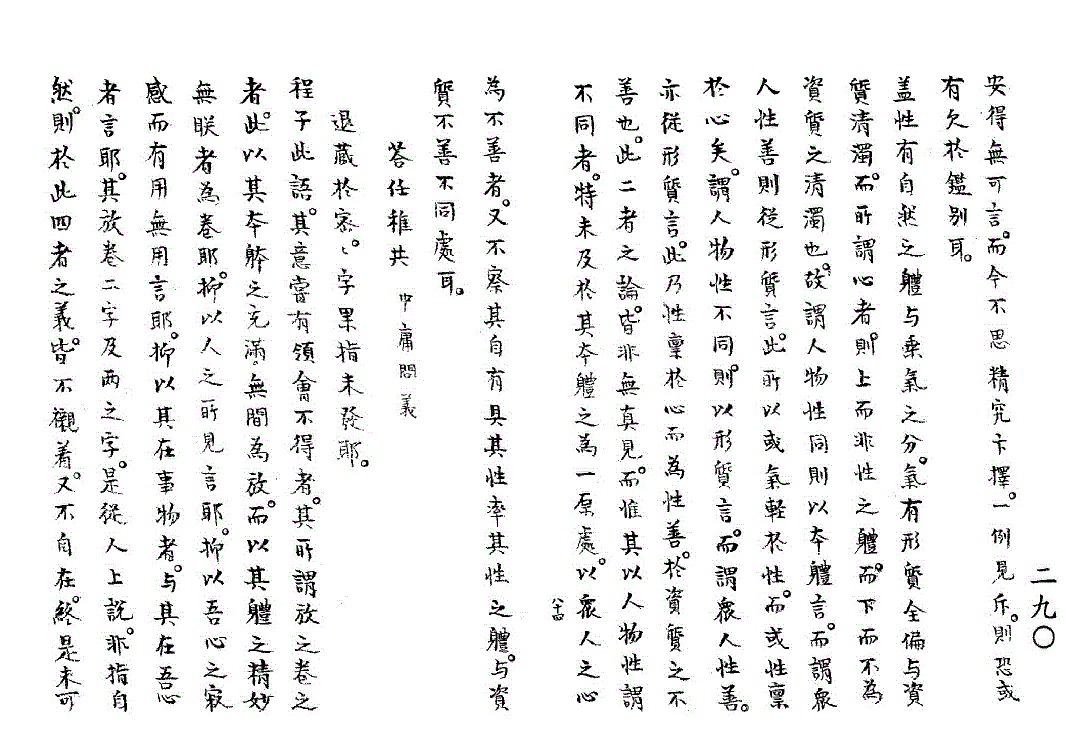 安得无可言。而今不思精究卞择。一例见斥。则恐或有欠于鉴别耳。
安得无可言。而今不思精究卞择。一例见斥。则恐或有欠于鉴别耳。盖性有自然之体与乘气之分。气有形质全偏与资质清浊。而所谓心者。则上而非性之体。而下而不为资质之清浊也。故谓人物性同则以本体言。而谓众人性善则从形质言。此所以或气轻于性。而或性禀于心矣。谓人物性不同。则以形质言。而谓众人性善。亦从形质言。此乃性禀于心而为性善。于资质之不善也。此二者之论。皆非无真见。而惟其以人物性谓不同者。特未及于其本体之为一原处。以众人之心为不善者。又不察其自有具其性率其性之体。与资质不善不同处耳。
答任稚共(中庸问义)
退藏于密。密字果指未发耶。
程子此语。其意尝有领会不得者。其所谓放之卷之者。此以其本体之充满无间为放。而以其体之精妙无眹者为卷耶。抑以人之所见言耶。抑以吾心之寂感而有用无用言耶。抑以其在事物者。与其在吾心者言耶。其放卷二字及两之字。是从人上说。非指自然。则于此四者之义。皆不衬着。又不自在。终是未可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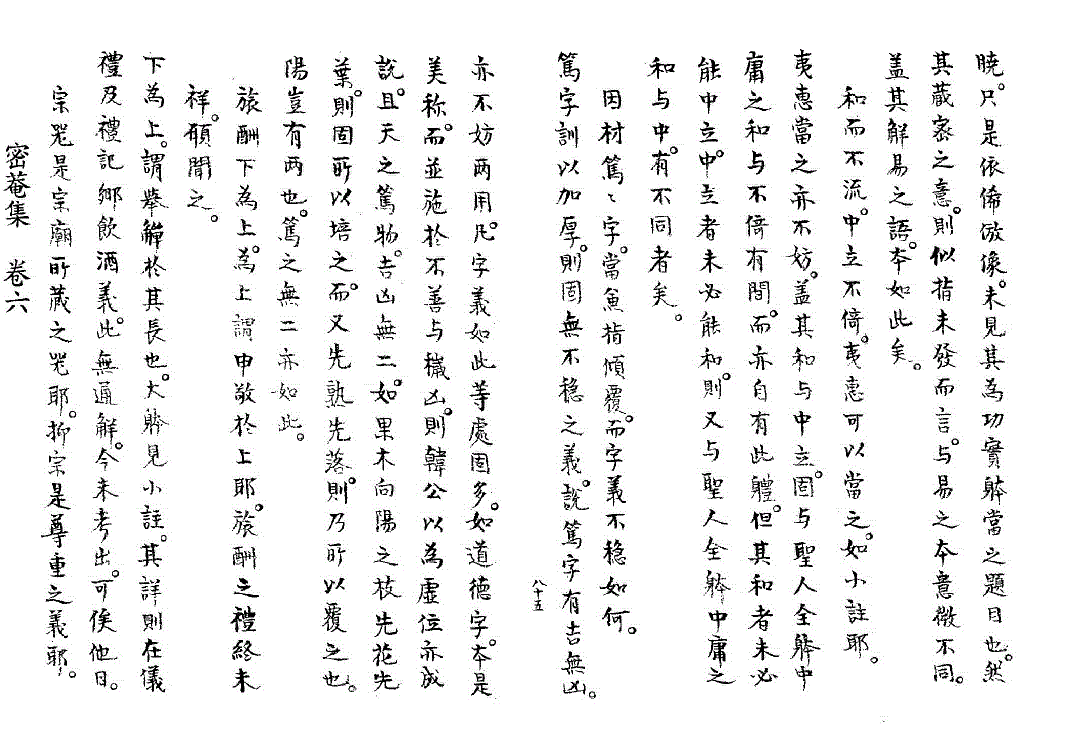 晓。只是依俙仿像。未见其为功实体当之题目也。然其藏密之意。则似指未发而言。与易之本意微不同。盖其解易之语。本如此矣。
晓。只是依俙仿像。未见其为功实体当之题目也。然其藏密之意。则似指未发而言。与易之本意微不同。盖其解易之语。本如此矣。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夷惠可以当之。如小注耶。
夷惠当之亦不妨。盖其和与中立。固与圣人全体中庸之和与不倚有间。而亦自有此体。但其和者未必能中立。中立者未必能和。则又与圣人全体中庸之和与中。有不同者矣。
因材笃笃字。当兼指倾覆。而字义不稳如何。
笃字训以加厚。则固无不稳之义。说笃字有吉无凶。亦不妨两用。凡字义如此等处固多。如道德字。本是美称。而并施于不善与秽凶。则韩公以为虚位亦成说。且天之笃物。吉凶无二。如果木向阳之枝先花先叶。则固所以培之。而又先熟先落。则乃所以覆之也。阳岂有两也。笃之无二亦如此。
旅酬下为上。为上谓申敬于上耶。旅酬之礼终未祥。愿闻之。
下为上。谓举觯于其长也。大体见小注。其详则在仪礼及礼记乡饮酒义。此无通解。今未考出。可俟他日。
宗器是宗庙所藏之器耶。抑宗是尊重之义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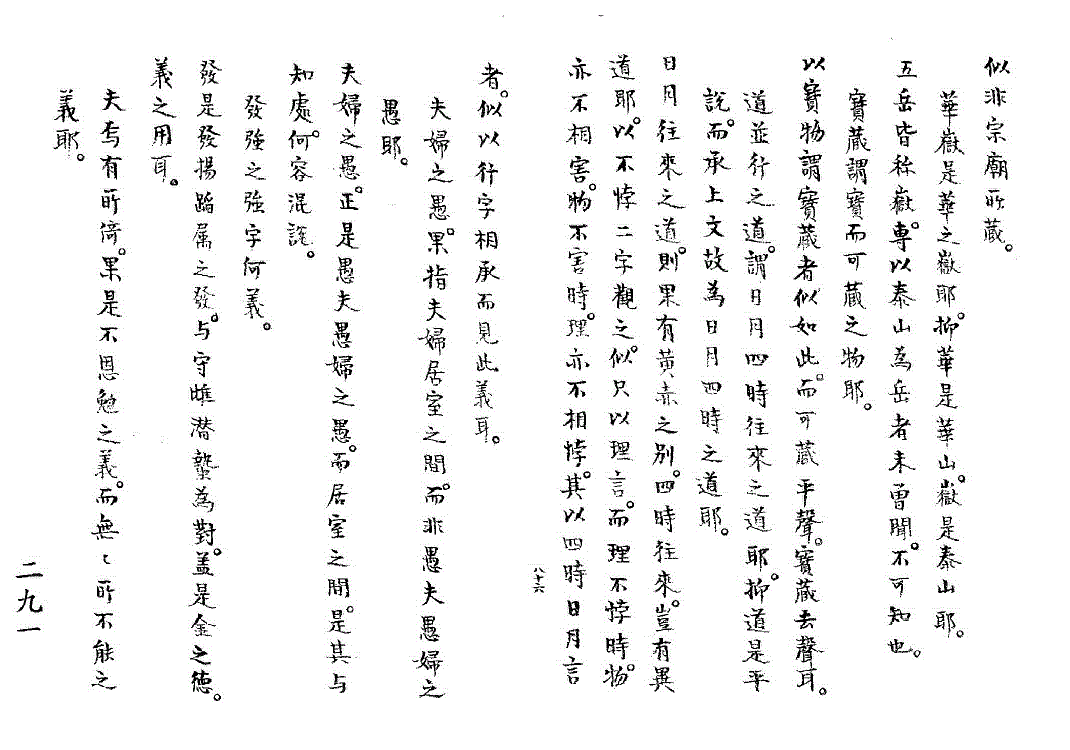 似非宗庙所藏。
似非宗庙所藏。华岳是华之岳耶。抑华是华山。岳是泰山耶。
五岳皆称岳。专以泰山为岳者未曾闻。不可知也。
宝藏谓宝而可藏之物耶。
以宝物谓宝藏者似如此。而可藏平声。宝藏去声耳。
道并行之道。谓日月四时往来之道耶。抑道是平说。而承上文故为日月四时之道耶。
日月往来之道。则果有黄赤之别。四时往来。岂有异道耶。以不悖二字观之。似只以理言。而理不悖时。物亦不相害。物不害时。理亦不相悖。其以四时日月言者。似以行字相承而见此义耳。
夫妇之愚。果指夫妇居室之间。而非愚夫愚妇之愚耶。
夫妇之愚。正是愚夫愚妇之愚。而居室之间。是其与知处。何容混说。
发强之强字何义。
发是发扬蹈属之发。与守雌潜蛰为对。盖是金之德。义之用耳。
夫焉有所倚。果是不恩勉之义。而无无所不能之义耶。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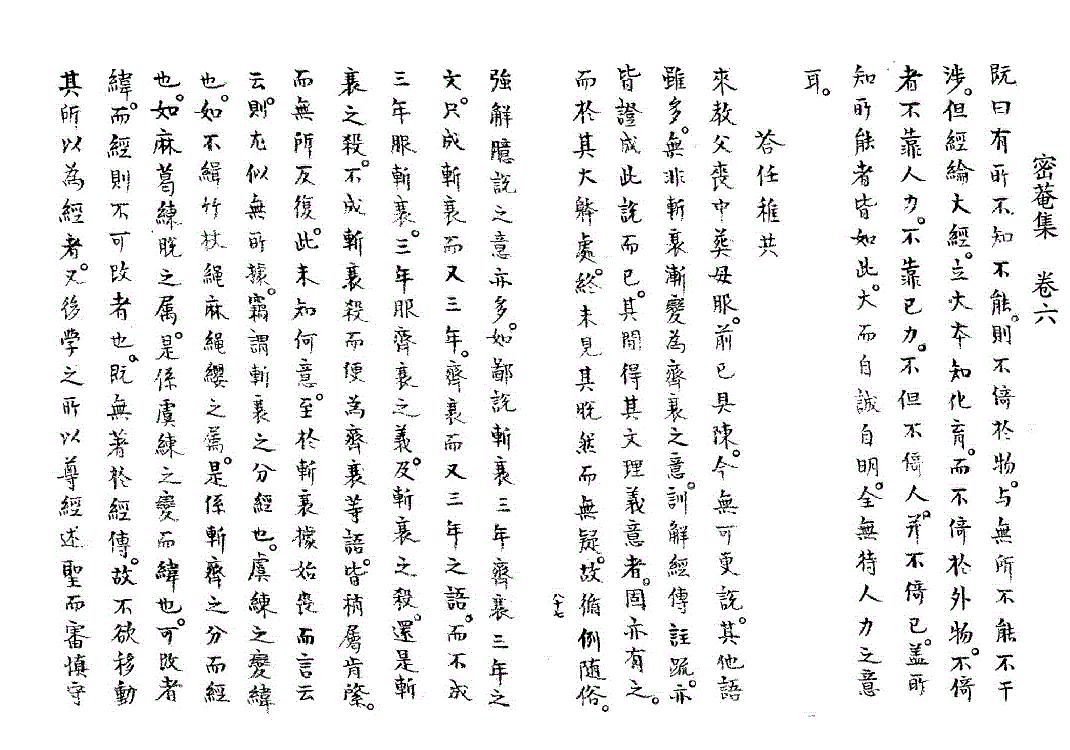 既曰有所不知不能。则不倚于物。与无所不能不干涉。但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而不倚于外物。不倚者不靠人力。不靠己力。不但不倚人。并不倚己。盖所知所能者皆如此。大而自诚自明。全无待人力之意耳。
既曰有所不知不能。则不倚于物。与无所不能不干涉。但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而不倚于外物。不倚者不靠人力。不靠己力。不但不倚人。并不倚己。盖所知所能者皆如此。大而自诚自明。全无待人力之意耳。答任稚共
来教父丧中葬母服。前已具陈。今无可更说。其他语虽多。无非斩衰渐变为齐衰之意。训解经传注疏。亦皆證成此说而已。其间得其文理义意者。固亦有之。而于其大体处。终未见其脱然而无疑。故循例随俗。强解臆说之意亦多。如鄙说斩衰三年齐衰三年之文。只成斩衰而又三年。齐衰而又三年之语。而不成三年服斩衰。三年服齐衰之义。及斩衰之杀。还是斩衰之杀。不成斩衰杀而便为齐衰等语。皆稍属肯綮。而无所反复。此未知何意。至于斩衰据始丧而言云云。则尤似无所据。窃谓斩衰之分经也。虞练之变纬也。如不缉竹杖绳麻绳缨之属。是系斩齐之分而经也。如麻葛练脱之属。是系虞练之变而纬也。可改者纬。而经则不可改者也。既无著于经传。故不欲移动其所以为经者。又后学之所以尊经述圣而审慎守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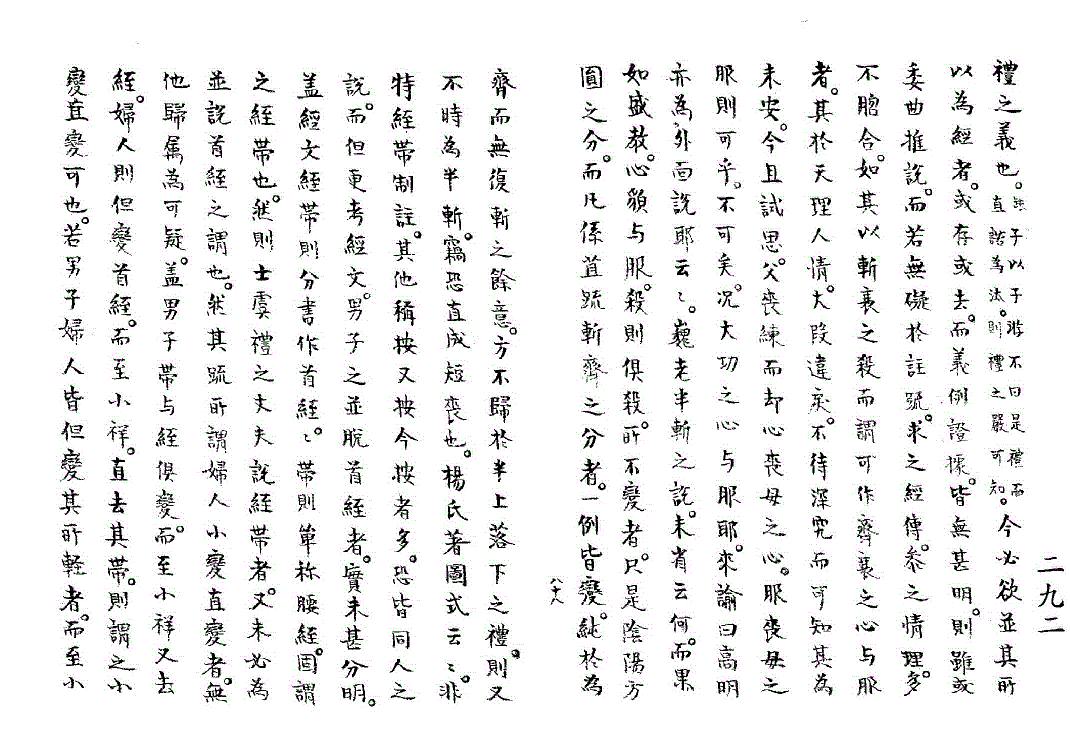 礼之义也。(缺子以子游不曰是礼而直诺为汰。则礼之严可知。)今必欲并其所以为经者。或存或去。而义例證据。皆无甚明。则虽或委曲推说。而若无碍于注疏。求之经传。参之情理。多不吻合。如其以斩衰之杀而谓可作齐衰之心与服者。其于天理人情。大段违戾。不待深究而可知其为未安。今且试思。父丧练而却心丧母之心。服丧母之服则可乎。不可矣。况大功之心与服耶。来谕曰高明亦为外面说耶云云。巍老半斩之说。未省云何。而果如盛教。心貌与服。杀则俱杀。所不变者。只是阴阳方圆之分。而凡系苴疏斩齐之分者。一例皆变。纯于为齐而无复斩之馀意。方不归于半上落下之礼。则又不时为半斩。窃恐直成短丧也。杨氏著图式云云。非特绖带制注。其他称按又按今按者多。恐皆同人之说。而但更考经文。男子之并脱首绖者。实未甚分明。盖经文绖带则分书作首绖。绖带则单称腰绖。固谓之绖带也。然则士虞礼之丈夫说绖带者。又未必为并说首绖之谓也。然其疏所谓妇人小变直变者。无他归属为可疑。盖男子带与绖俱变。而至小祥又去绖。妇人则但变首绖。而至小祥。直去其带。则谓之小变直变可也。若男子妇人皆但变其所轻者。而至小
礼之义也。(缺子以子游不曰是礼而直诺为汰。则礼之严可知。)今必欲并其所以为经者。或存或去。而义例證据。皆无甚明。则虽或委曲推说。而若无碍于注疏。求之经传。参之情理。多不吻合。如其以斩衰之杀而谓可作齐衰之心与服者。其于天理人情。大段违戾。不待深究而可知其为未安。今且试思。父丧练而却心丧母之心。服丧母之服则可乎。不可矣。况大功之心与服耶。来谕曰高明亦为外面说耶云云。巍老半斩之说。未省云何。而果如盛教。心貌与服。杀则俱杀。所不变者。只是阴阳方圆之分。而凡系苴疏斩齐之分者。一例皆变。纯于为齐而无复斩之馀意。方不归于半上落下之礼。则又不时为半斩。窃恐直成短丧也。杨氏著图式云云。非特绖带制注。其他称按又按今按者多。恐皆同人之说。而但更考经文。男子之并脱首绖者。实未甚分明。盖经文绖带则分书作首绖。绖带则单称腰绖。固谓之绖带也。然则士虞礼之丈夫说绖带者。又未必为并说首绖之谓也。然其疏所谓妇人小变直变者。无他归属为可疑。盖男子带与绖俱变。而至小祥又去绖。妇人则但变首绖。而至小祥。直去其带。则谓之小变直变可也。若男子妇人皆但变其所轻者。而至小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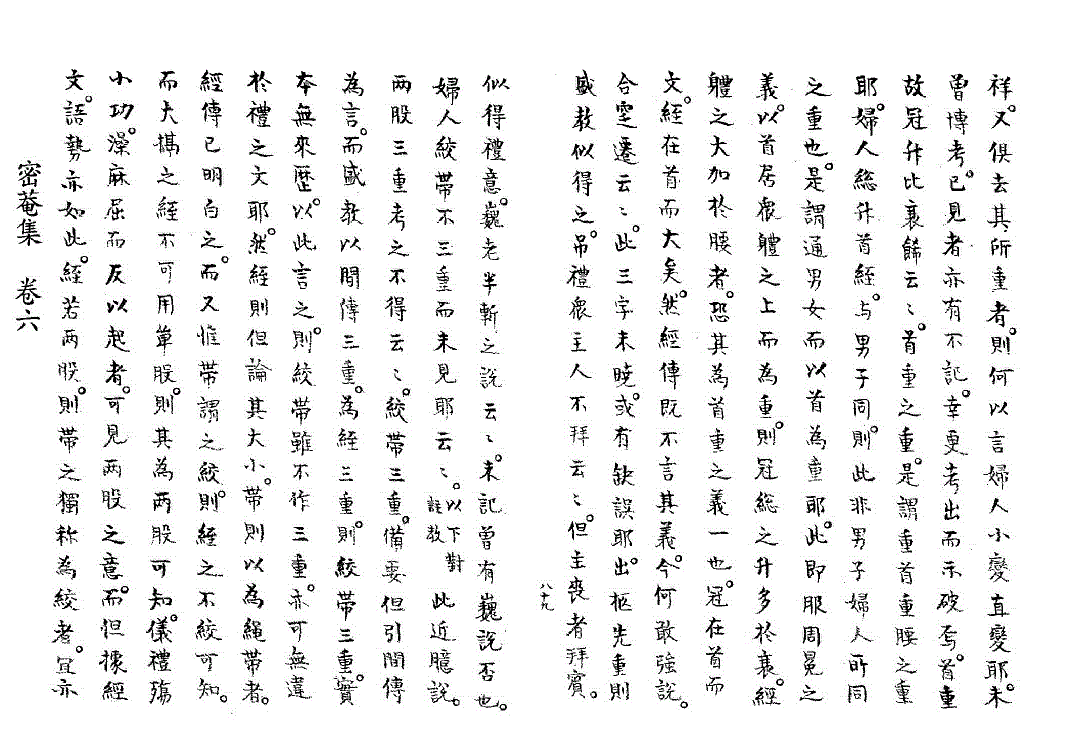 祥。又俱去其所重者。则何以言妇人小变直变耶。未曾博考。已见者亦有不记。幸更考出而示破焉。首重故冠升比衰饰云云。首重之重。是谓重首重腰之重耶。妇人总升首绖。与男子同。则此非男子妇人所同之重也。是谓通男女而以首为重耶。此即服周冕之义。以首居众体之上而为重。则冠总之升多于衰。经体之大加于腰者。恐其为首重之义一也。冠在首而文。绖在首而大矣。然经传既不言其义。今何敢强说。合窆迁云云。此三字未晓。或有缺误耶。出柩先重则盛教似得之。吊礼众主人不拜云云。但主丧者拜宾。似得礼意。巍老半斩之说云云。未记曾有巍说否也。妇人绞带不三重而未见耶云云。(以下对注教)此近臆说。两股三重考之不得云云。绞带三重。备要但引间传为言。而盛教以间传三重。为绖三重。则绞带三重。实本无来历。以此言之。则绞带虽不作三重。亦可无违于礼之文耶。然绖则但论其大小。带则以为绳带者。经传已明白之。而又惟带谓之绞。则绖之不绞可知。而大扼之绖不可用单股。则其为两股可知。仪礼殇小功。澡麻屈而反以起者。可见两股之意。而但据经文。语势亦如此。绖若两股。则带之独称为绞者。宜亦
祥。又俱去其所重者。则何以言妇人小变直变耶。未曾博考。已见者亦有不记。幸更考出而示破焉。首重故冠升比衰饰云云。首重之重。是谓重首重腰之重耶。妇人总升首绖。与男子同。则此非男子妇人所同之重也。是谓通男女而以首为重耶。此即服周冕之义。以首居众体之上而为重。则冠总之升多于衰。经体之大加于腰者。恐其为首重之义一也。冠在首而文。绖在首而大矣。然经传既不言其义。今何敢强说。合窆迁云云。此三字未晓。或有缺误耶。出柩先重则盛教似得之。吊礼众主人不拜云云。但主丧者拜宾。似得礼意。巍老半斩之说云云。未记曾有巍说否也。妇人绞带不三重而未见耶云云。(以下对注教)此近臆说。两股三重考之不得云云。绞带三重。备要但引间传为言。而盛教以间传三重。为绖三重。则绞带三重。实本无来历。以此言之。则绞带虽不作三重。亦可无违于礼之文耶。然绖则但论其大小。带则以为绳带者。经传已明白之。而又惟带谓之绞。则绖之不绞可知。而大扼之绖不可用单股。则其为两股可知。仪礼殇小功。澡麻屈而反以起者。可见两股之意。而但据经文。语势亦如此。绖若两股。则带之独称为绞者。宜亦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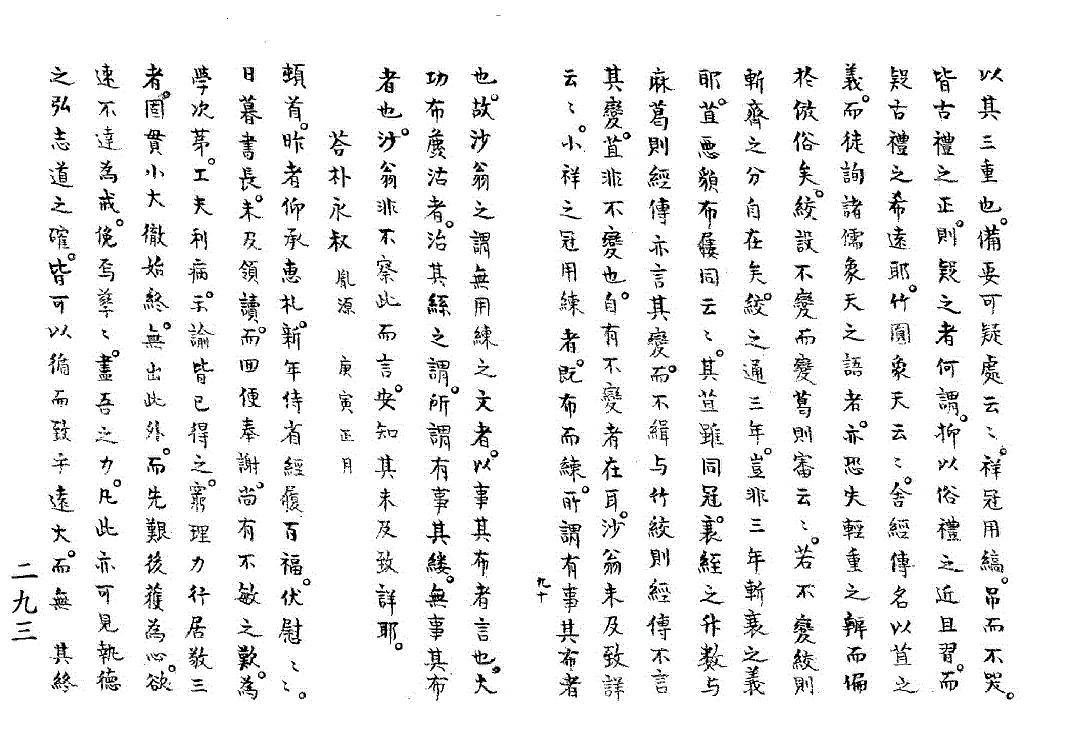 以其三重也。备要可疑处云云。祥冠用缟。吊而不哭。皆古礼之正。则疑之者何谓。抑以俗礼之近且习。而疑古礼之希远耶。竹圆象天云云。舍经传名以苴之义。而徒询诸儒象天之语者。亦恐失轻重之辨而偏于仿俗矣。绞设不变而变葛则审云云。若不变绞则斩齐之分自在矣。绞之通三年。岂非三年斩衰之义耶。苴恶貌布屦同云云。其苴虽同冠。衰绖之升数与麻葛则经传亦言其变。而不缉与竹绞则经传不言其变。苴非不变也。自有不变者在耳。沙翁未及致详云云。小祥之冠用练者。既布而练。所谓有事其布者也。故沙翁之谓无用练之文者。以事其布者言也。大功布粗沽者。治其丝之谓。所谓有事其缕。无事其布者也。沙翁非不察此而言。安知其未及致详耶。
以其三重也。备要可疑处云云。祥冠用缟。吊而不哭。皆古礼之正。则疑之者何谓。抑以俗礼之近且习。而疑古礼之希远耶。竹圆象天云云。舍经传名以苴之义。而徒询诸儒象天之语者。亦恐失轻重之辨而偏于仿俗矣。绞设不变而变葛则审云云。若不变绞则斩齐之分自在矣。绞之通三年。岂非三年斩衰之义耶。苴恶貌布屦同云云。其苴虽同冠。衰绖之升数与麻葛则经传亦言其变。而不缉与竹绞则经传不言其变。苴非不变也。自有不变者在耳。沙翁未及致详云云。小祥之冠用练者。既布而练。所谓有事其布者也。故沙翁之谓无用练之文者。以事其布者言也。大功布粗沽者。治其丝之谓。所谓有事其缕。无事其布者也。沙翁非不察此而言。安知其未及致详耶。答朴永叔(胤源○庚寅正月)
顿首。昨者仰承惠札。新年侍省经履百福。伏慰伏慰。日暮书长。未及领读。而回便奉谢。尚有不敏之叹。为学次第。工夫利病。示谕皆已得之。穷理力行居敬三者。固贯小大彻始终。无出此外。而先艰后获为心。欲速不达为戒。俛焉孳孳。尽吾之力。凡此亦可见执德之弘志道之确。皆可以循而致乎远大。而无▣其终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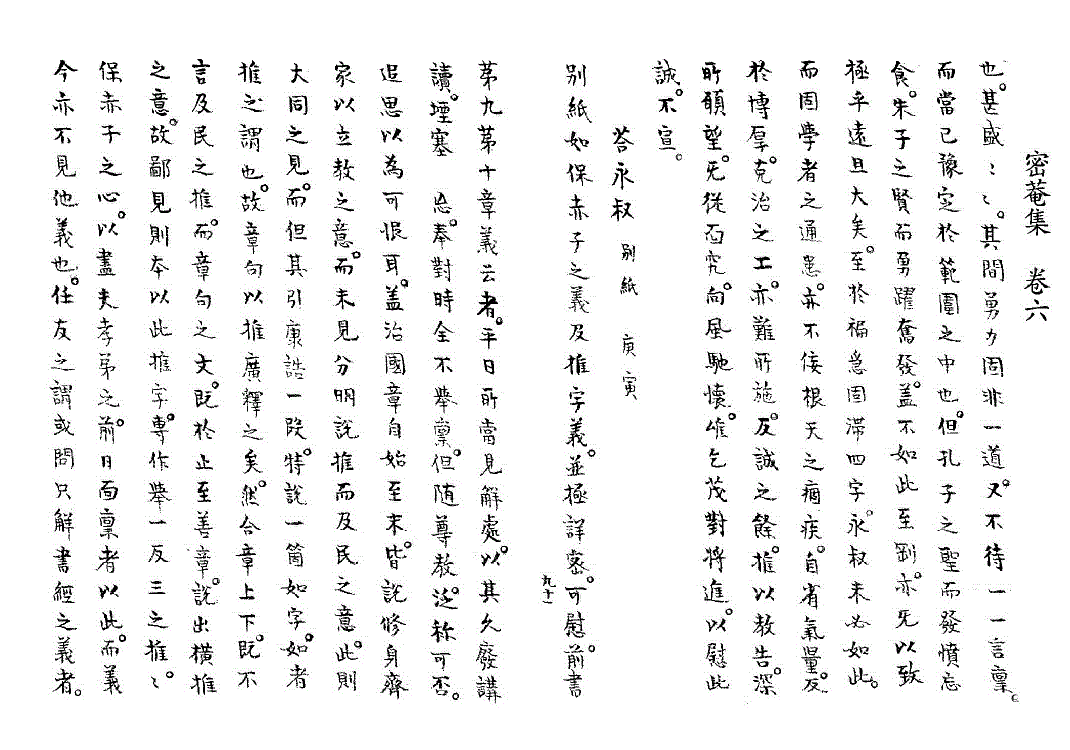 也。甚盛甚盛。其间勇力固非一道。又不待一一言禀。而当已豫定于范围之中也。但孔子之圣而发愤忘食。朱子之贤而勇跃奋发。盖不如此至刚。亦无以致极乎远且大矣。至于褊急固滞四字。永叔未必如此。而固学者之通患。亦不佞根天之痼疾。自省气量。反于博厚。克治之工。亦难所施。反诚之馀。推以教告。深所愿望。无从面究。向风驰怀。唯乞茂对将进。以慰此诚。不宣。
也。甚盛甚盛。其间勇力固非一道。又不待一一言禀。而当已豫定于范围之中也。但孔子之圣而发愤忘食。朱子之贤而勇跃奋发。盖不如此至刚。亦无以致极乎远且大矣。至于褊急固滞四字。永叔未必如此。而固学者之通患。亦不佞根天之痼疾。自省气量。反于博厚。克治之工。亦难所施。反诚之馀。推以教告。深所愿望。无从面究。向风驰怀。唯乞茂对将进。以慰此诚。不宣。答永叔(别纸○庚寅)
别纸如保赤子之义及推字义。并极详密。可慰。前书第九第十章义云者。平日所当见解处。以其久废讲读。堙塞▣忘。奉对时全不举禀。但随尊教。泛称可否。追思以为可恨耳。盖治国章自始至末。皆说修身齐家以立教之意。而未见分明说推而及民之意。此则大同之见。而但其引康诰一段。特说一个如字。如者推之谓也。故章句以推广释之矣。然合章上下。既不言及民之推。而章句之文。既于止至善章。说出横推之意。故鄙见则本以此推字。专作举一反三之推。推保赤子之心。以尽夫孝弟之。前日面禀者以此。而义今亦不见他义也。任友之谓或问只解书经之义者。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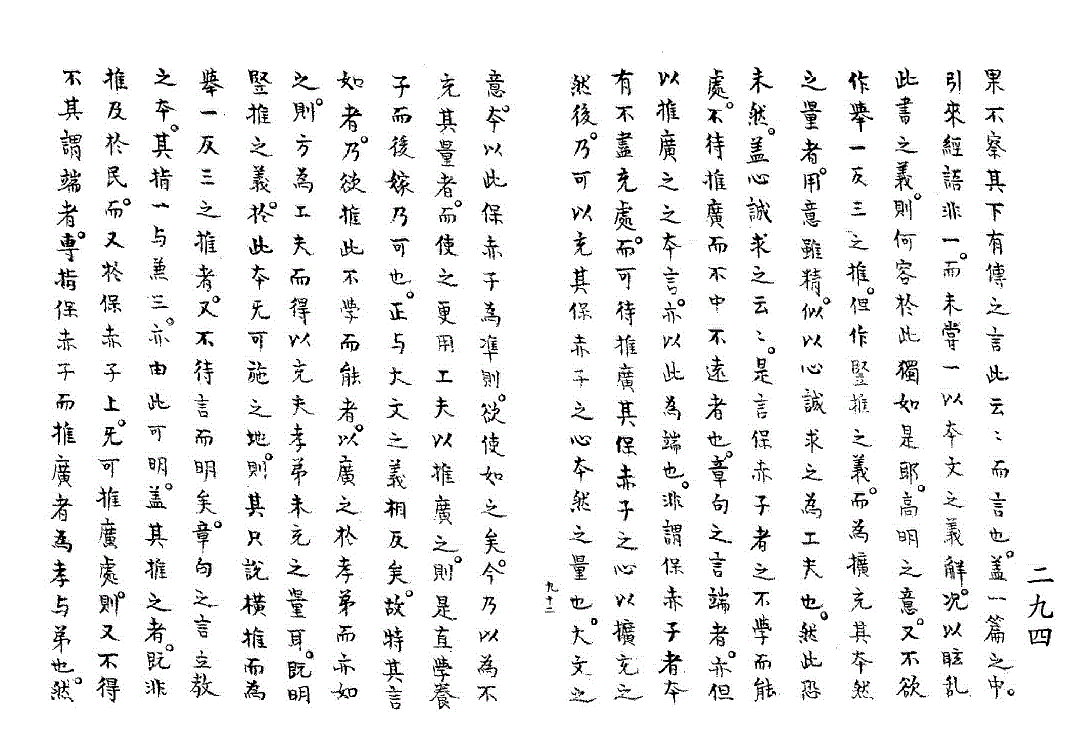 果不察其下有传之言此云云而言也。盖一篇之中。引来经语非一。而未尝一以本文之义解。况以眩乱此书之义。则何容于此独如是耶。高明之意。又不欲作举一反三之推。但作竖推之义。而为扩充其本然之量者。用意虽精。似以心诚求之为工夫也。然此恐未然。盖心诚求之云云。是言保赤子者之不学而能处。不待推广而不中不远者也。章句之言端者。亦但以推广之之本言。亦以此为端也。非谓保赤子者本有不尽充处。而可待推广其保赤子之心以扩充之然后。乃可以充其保赤子之心本然之量也。大文之意。本以此保赤子为准则。欲使如之矣。今乃以为不充其量者。而使之更用工夫以推广之。则是直学养子而后嫁乃可也。正与大文之义相反矣。故特其言如者。乃欲推此不学而能者。以广之于孝弟而亦如之。则方为工夫而得以充夫孝弟未充之量耳。既明竖推之义。于此本无可施之地。则其只说横推而为举一反三之推者。又不待言而明矣。章句之言立教之本。其指一与兼三。亦由此可明。盖其推之者。既非推及于民。而又于保赤子上。无可推广处。则又不得不其谓端者。专指保赤子而推广者为孝与弟也。然
果不察其下有传之言此云云而言也。盖一篇之中。引来经语非一。而未尝一以本文之义解。况以眩乱此书之义。则何容于此独如是耶。高明之意。又不欲作举一反三之推。但作竖推之义。而为扩充其本然之量者。用意虽精。似以心诚求之为工夫也。然此恐未然。盖心诚求之云云。是言保赤子者之不学而能处。不待推广而不中不远者也。章句之言端者。亦但以推广之之本言。亦以此为端也。非谓保赤子者本有不尽充处。而可待推广其保赤子之心以扩充之然后。乃可以充其保赤子之心本然之量也。大文之意。本以此保赤子为准则。欲使如之矣。今乃以为不充其量者。而使之更用工夫以推广之。则是直学养子而后嫁乃可也。正与大文之义相反矣。故特其言如者。乃欲推此不学而能者。以广之于孝弟而亦如之。则方为工夫而得以充夫孝弟未充之量耳。既明竖推之义。于此本无可施之地。则其只说横推而为举一反三之推者。又不待言而明矣。章句之言立教之本。其指一与兼三。亦由此可明。盖其推之者。既非推及于民。而又于保赤子上。无可推广处。则又不得不其谓端者。专指保赤子而推广者为孝与弟也。然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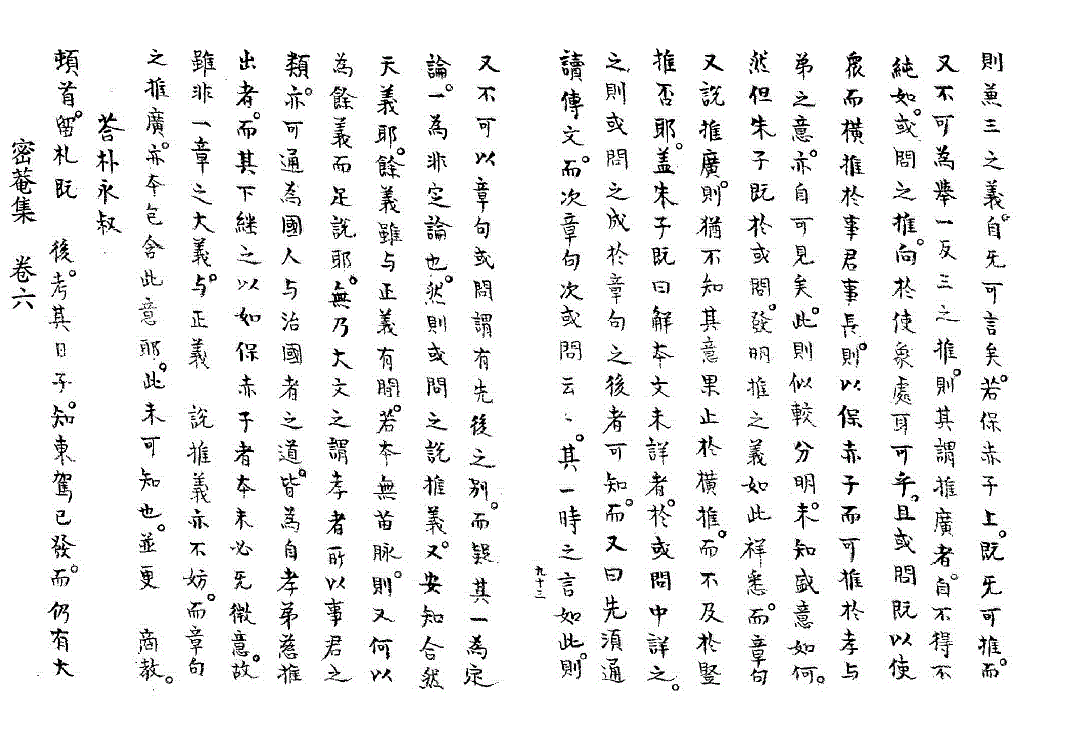 则兼三之义。自无可言矣。若保赤子上。既无可推。而又不可为举一反三之推。则其谓推广者。自不得不纯如。或问之推。向于使象处耳可乎。且或问既以使众而横推于事君事长。则以保赤子而可推于孝与弟之意。亦自可见矣。此则似较分明。未知盛意如何。然但朱子既于或问。发明推之义如此祥悉。而章句又说推广。则犹不知其意果止于横推。而不及于竖推否耶。盖朱子既曰解本文未详者。于或问中详之。之则或问之成于章句之后者可知。而又曰先须通读传文。而次章句次或问云云。其一时之言如此。则又不可以章句或问谓有先后之别。而疑其一为定论。一为非定论也。然则或问之说推义。又安知合然天义耶。馀义虽与正义有间。若本无苗脉。则又何以为馀义而足说耶。无乃大文之谓孝者所以事君之类。亦可通为国人与治国者之道。皆为自孝弟慈推出者。而其下继之以如保赤子者本未必无微意。故虽非一章之大义。与正义▣说推义亦不妨。而章句之推广。亦本包含此意耶。此未可知也。并更▣商教。
则兼三之义。自无可言矣。若保赤子上。既无可推。而又不可为举一反三之推。则其谓推广者。自不得不纯如。或问之推。向于使象处耳可乎。且或问既以使众而横推于事君事长。则以保赤子而可推于孝与弟之意。亦自可见矣。此则似较分明。未知盛意如何。然但朱子既于或问。发明推之义如此祥悉。而章句又说推广。则犹不知其意果止于横推。而不及于竖推否耶。盖朱子既曰解本文未详者。于或问中详之。之则或问之成于章句之后者可知。而又曰先须通读传文。而次章句次或问云云。其一时之言如此。则又不可以章句或问谓有先后之别。而疑其一为定论。一为非定论也。然则或问之说推义。又安知合然天义耶。馀义虽与正义有间。若本无苗脉。则又何以为馀义而足说耶。无乃大文之谓孝者所以事君之类。亦可通为国人与治国者之道。皆为自孝弟慈推出者。而其下继之以如保赤子者本未必无微意。故虽非一章之大义。与正义▣说推义亦不妨。而章句之推广。亦本包含此意耶。此未可知也。并更▣商教。答朴永叔
顿首。留札既▣后。考其日子。知东驾已发。而仍有大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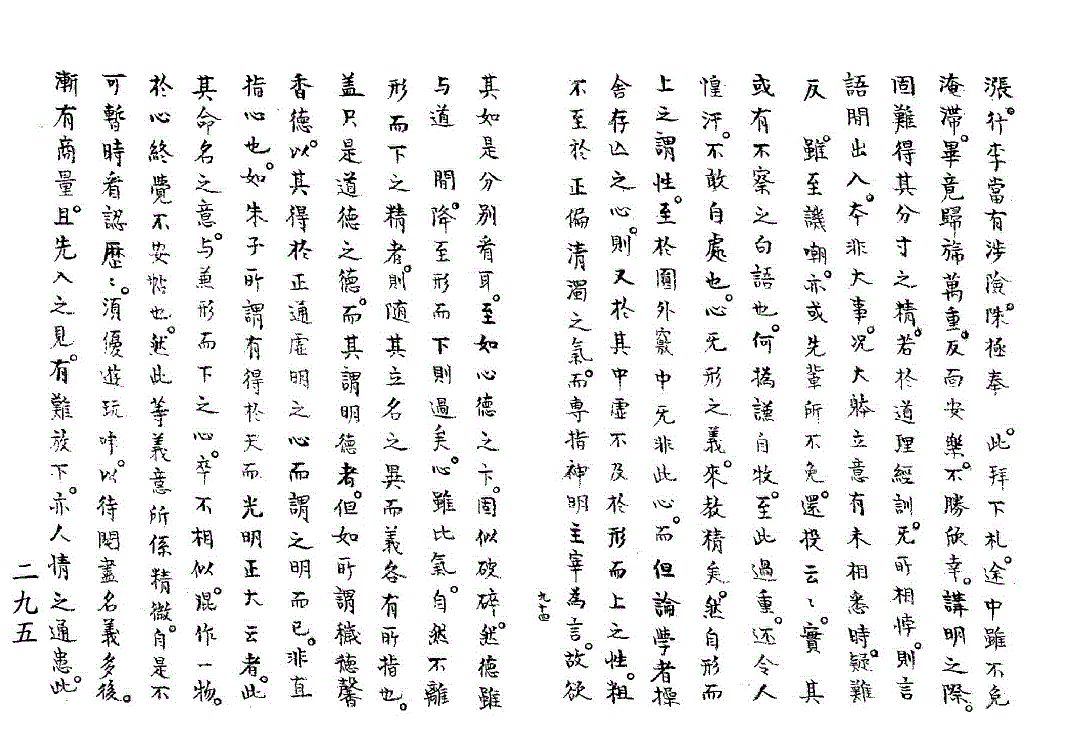 涨。行李当有涉险。陎极奉▣。此拜下札。途中虽不免淹滞。毕竟归旆万重。反面安乐。不胜欣幸。讲明之际。固难得其分寸之精。若于道理经训。无所相悖。则言语间出入。本非大事。况大体立意有未相悉时。疑难反▣。虽至讥嘲。亦或先辈所不免。还投云云。实▣其或有不察之句语也。何撝谦自牧。至此过重。还令人惶汗。不敢自处也。心无形之义。来教精矣。然自形而上之谓性。至于圆外窍中无非此心。而但论学者操舍存亡之心。则又于其中虚不及于形而上之性。粗不至于正偏清浊之气。而专指神明主宰为言。故欲其如是分别看耳。至如心德之卞。固似破碎。然德虽与道▣间。降至形而下则过矣。心虽比气。自然不离形而下之精者。则随其立名之异而义各有所指也。盖只是道德之德。而其谓明德者。但如所谓秽德馨香德。以其得于正通虚明之心而谓之明而已。非直指心也。如朱子所谓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云者。此其命名之意。与兼形而下之心。卒不相似。混作一物。于心终觉不安帖也。然此等义意所系精微。自是不可暂时看认历历。须优游玩味。以待阅尽名义多后。渐有商量。且先入之见。有难放下。亦人情之通患。此
涨。行李当有涉险。陎极奉▣。此拜下札。途中虽不免淹滞。毕竟归旆万重。反面安乐。不胜欣幸。讲明之际。固难得其分寸之精。若于道理经训。无所相悖。则言语间出入。本非大事。况大体立意有未相悉时。疑难反▣。虽至讥嘲。亦或先辈所不免。还投云云。实▣其或有不察之句语也。何撝谦自牧。至此过重。还令人惶汗。不敢自处也。心无形之义。来教精矣。然自形而上之谓性。至于圆外窍中无非此心。而但论学者操舍存亡之心。则又于其中虚不及于形而上之性。粗不至于正偏清浊之气。而专指神明主宰为言。故欲其如是分别看耳。至如心德之卞。固似破碎。然德虽与道▣间。降至形而下则过矣。心虽比气。自然不离形而下之精者。则随其立名之异而义各有所指也。盖只是道德之德。而其谓明德者。但如所谓秽德馨香德。以其得于正通虚明之心而谓之明而已。非直指心也。如朱子所谓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云者。此其命名之意。与兼形而下之心。卒不相似。混作一物。于心终觉不安帖也。然此等义意所系精微。自是不可暂时看认历历。须优游玩味。以待阅尽名义多后。渐有商量。且先入之见。有难放下。亦人情之通患。此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2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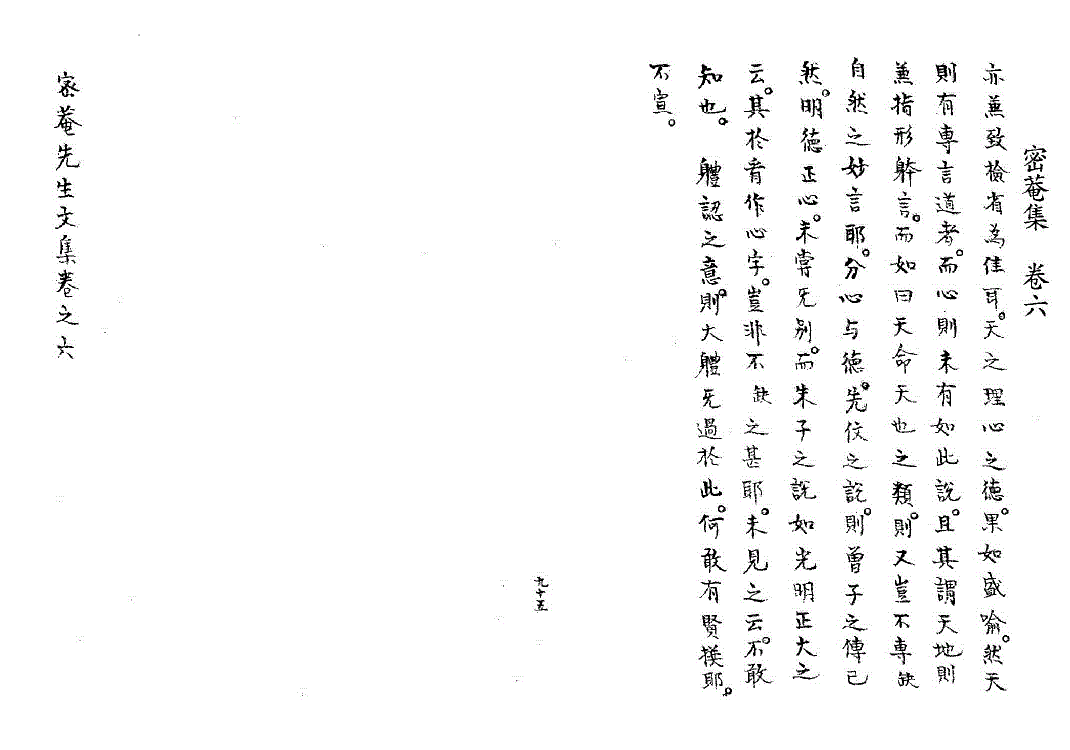 亦兼致检省为佳耳。天之理心之德。果如盛喻。然天则有专言道者。而心则未有如此说。且其谓天地则兼指形体言。而如曰天命天也之类。则又岂不专(缺)自然之妙言耶。分心与德。先伩之说。则曾子之传已然。明德正心。未尝无别。而朱子之说如光明正大之云。其于看作心字。岂非不(缺)之甚耶。未见之云。不敢知也。▣体认之意。则大体无过于此。何敢有贤撰耶。不宣。
亦兼致检省为佳耳。天之理心之德。果如盛喻。然天则有专言道者。而心则未有如此说。且其谓天地则兼指形体言。而如曰天命天也之类。则又岂不专(缺)自然之妙言耶。分心与德。先伩之说。则曾子之传已然。明德正心。未尝无别。而朱子之说如光明正大之云。其于看作心字。岂非不(缺)之甚耶。未见之云。不敢知也。▣体认之意。则大体无过于此。何敢有贤撰耶。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