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书
书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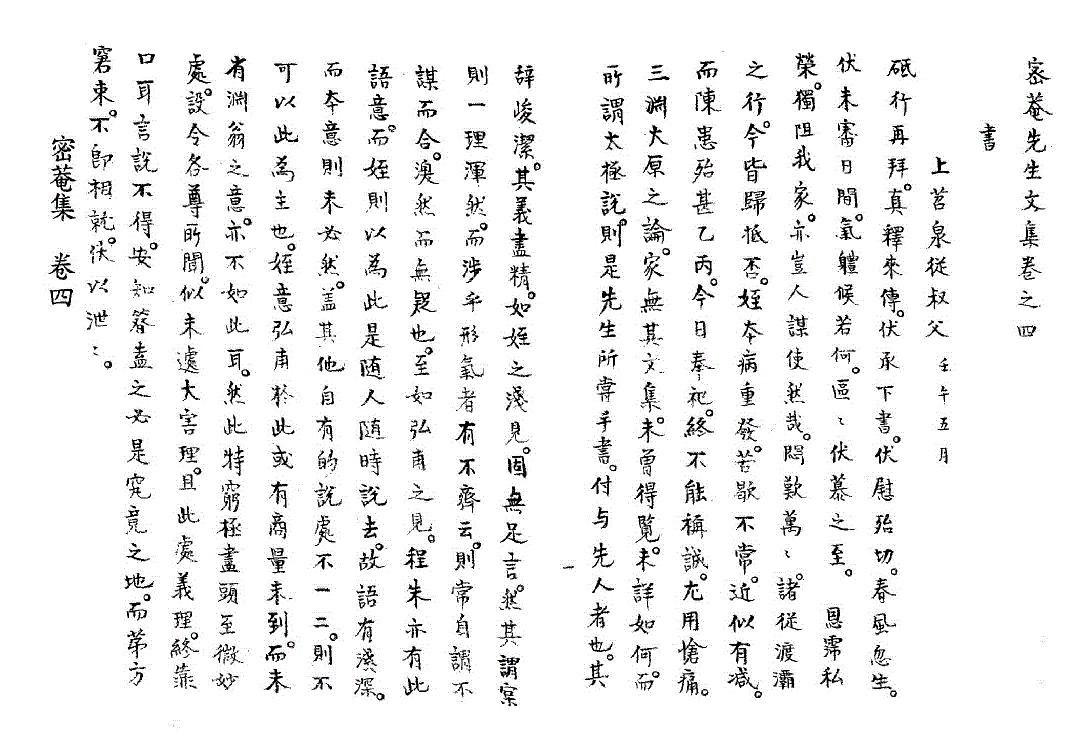 上苕泉从叔父(壬午五月)
上苕泉从叔父(壬午五月)砥行再拜。真释来传。伏承下书。伏慰殆切。春风忽生。伏未审日间。气体候若何。区区伏慕之至。 恩霈私荣。独阻我家。亦岂人谋使然哉。闷叹万万。诸从渡灞之行。今皆归抵否。侄本病重发。苦歇不常。近似有减。而陈患殆甚乙丙。今日奉祀。终不能称诚。尤用怆痛。三渊大原之论。家无其文集。未曾得览。未详如何。而所谓太极说。则是先生所尝手书。付与先人者也。其辞峻洁。其义尽精。如侄之浅见。固无足言。然其谓宲则一理浑然。而涉乎形气者有不齐云。则常自谓不谋而合。涣然而无疑也。至如弘甫之见。程朱亦有此语意。而侄则以为此是随人随时说去。故语有浅深。而本意则未必然。盖其他自有的说处不一二。则不可以此为主也。侄意弘甫于此或有商量未到。而未省渊翁之意。亦不如此耳。然此特穷极尽头至微妙处。设令各尊所闻。似未遽大害理。且此处义理。终靠口耳言说不得。安知簪盍之必是究竟之地。而第方窘束。不即相就。伏以泄泄。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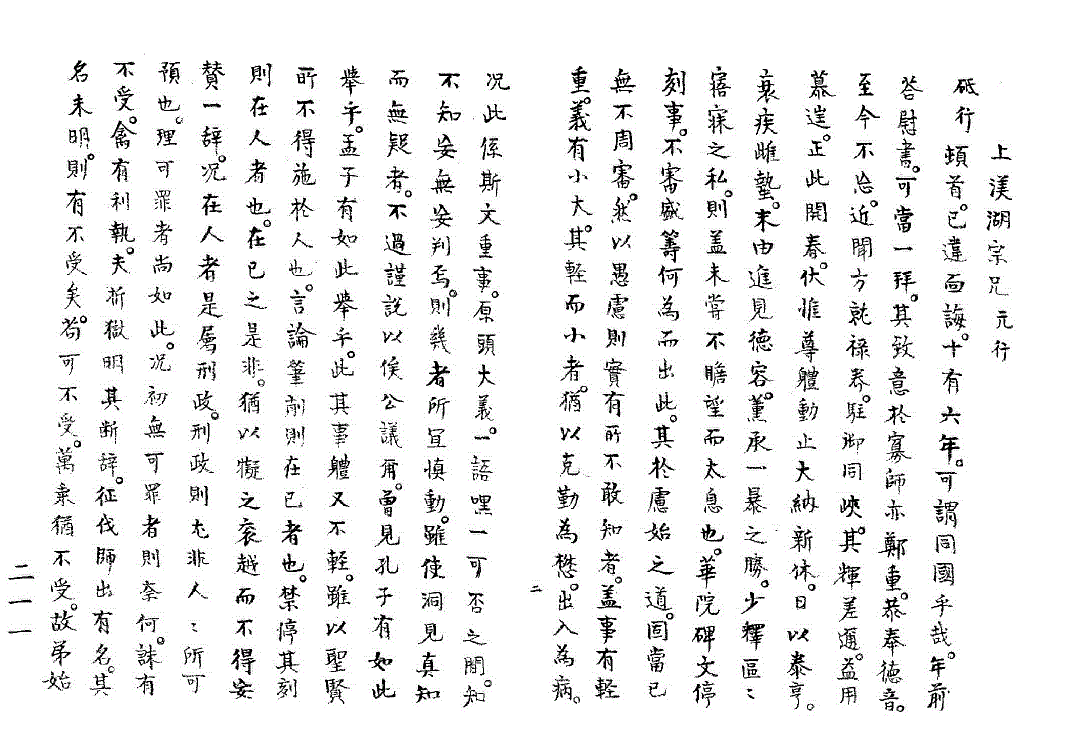 上渼湖宗兄(元行)
上渼湖宗兄(元行)砥行顿首。已违面诲。十有六年。可谓同国乎哉。年前答慰书。可当一拜。其致意于寡师亦郑重。恭奉德音。至今不忘。近闻方就禄养。驻御同峡。其辉差迩。益用慕𨓏。正此开春。伏惟尊体动止大纳新休。日以泰亨。衰疾雌蛰。末由进见德容。薰承一暴之胜。少释区区寤寐之私。则盖未尝不瞻望而太息也。华院碑文停刻事。不审盛筹何为而出此。其于虑始之道。固当已无不周审。然以愚虑则实有所不敢知者。盖事有轻重。义有小大。其轻而小者。犹以克勤为懋。出入为病。况此系斯文重事。原头大义。一语嘿一可否之间。知不知妄无妄判焉。则几者所宜慎动。虽使洞见真知而无疑者。不过谨说以俟公议尔。曾见孔子有如此举乎。孟子有如此举乎。此其事体又不轻。虽以圣贤所不得施于人也。言论笔削则在己者也。禁停其刻则在人者也。在己之是非。犹以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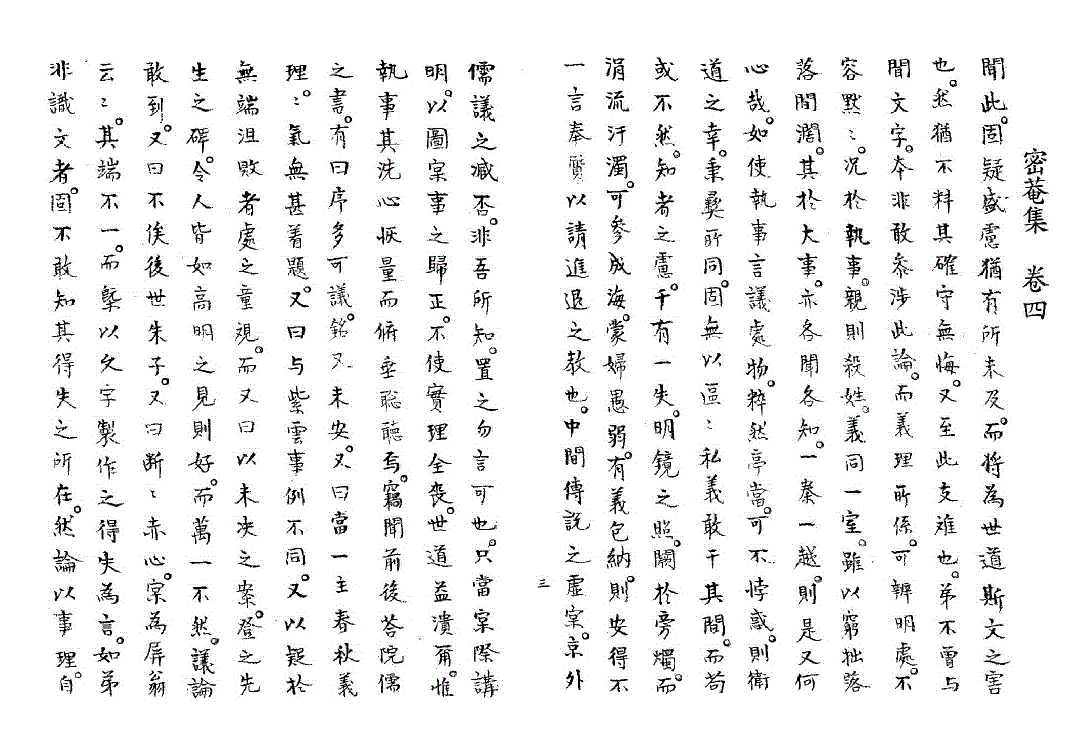 闻此。固疑盛虑犹有所未及。而将为世道斯文之害也。然犹不料其确守无悔。又至此支离也。弟不曾与闻文字。本非敢参涉此论。而义理所系。可辨明处。不容默默。况于执事。亲则杀姓。义同一室。虽以穷拙落落间阔。其于大事。亦各闻各知。一秦一越。则是又何心哉。如使执事言议处物。粹然亭当。可不悖惑。则卫道之幸。秉彝所同。固无以区区私义敢干其间。而苟或不然。知者之虑。千有一失。明镜之照。阙于旁烛。而涓流汗浊。可参成海。蒙妇愚弱。有义包纳。则安得不一言奉质以请进退之教也。中间传说之虚宲。京外儒议之臧否。非吾所知。置之勿言可也。只当宲际讲明。以图宲事之归正。不使实理全丧。世道益溃尔。惟执事其洗心恢量而俯垂聪听焉。窃闻前后答院儒之书。有曰序多可议。铭又未安。又曰当一主春秋义理。理气无甚着题。又曰与紫云事例不同。又以疑于无端沮败者处之童观。而又曰以未决之案。登之先生之碑。令人皆如高明之见则好。而万一不然。议论敢到。又曰不俟后世朱子。又曰断断赤心。宲为屏翁云云。其端不一。而槩以文字制作之得失为言。如弟非识文者。固不敢知其得失之所在。然论以事理。自
闻此。固疑盛虑犹有所未及。而将为世道斯文之害也。然犹不料其确守无悔。又至此支离也。弟不曾与闻文字。本非敢参涉此论。而义理所系。可辨明处。不容默默。况于执事。亲则杀姓。义同一室。虽以穷拙落落间阔。其于大事。亦各闻各知。一秦一越。则是又何心哉。如使执事言议处物。粹然亭当。可不悖惑。则卫道之幸。秉彝所同。固无以区区私义敢干其间。而苟或不然。知者之虑。千有一失。明镜之照。阙于旁烛。而涓流汗浊。可参成海。蒙妇愚弱。有义包纳。则安得不一言奉质以请进退之教也。中间传说之虚宲。京外儒议之臧否。非吾所知。置之勿言可也。只当宲际讲明。以图宲事之归正。不使实理全丧。世道益溃尔。惟执事其洗心恢量而俯垂聪听焉。窃闻前后答院儒之书。有曰序多可议。铭又未安。又曰当一主春秋义理。理气无甚着题。又曰与紫云事例不同。又以疑于无端沮败者处之童观。而又曰以未决之案。登之先生之碑。令人皆如高明之见则好。而万一不然。议论敢到。又曰不俟后世朱子。又曰断断赤心。宲为屏翁云云。其端不一。而槩以文字制作之得失为言。如弟非识文者。固不敢知其得失之所在。然论以事理。自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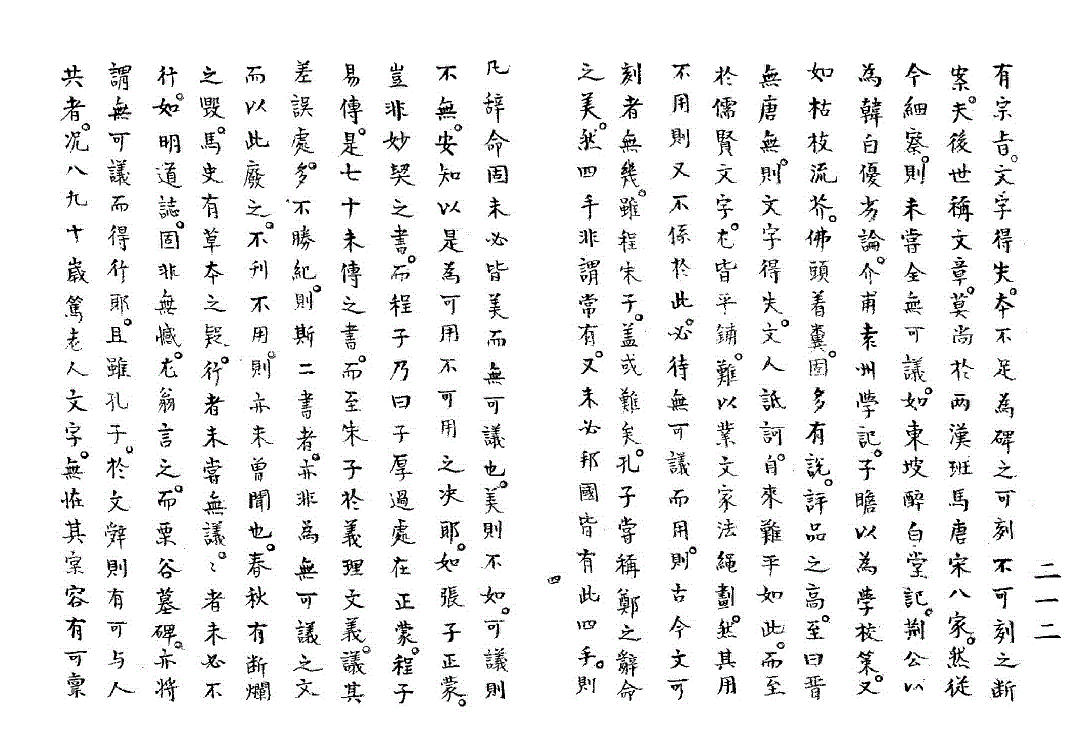 有宗旨。文字得失。本不足为碑之可刻不可刻之断案。夫后世称文章。莫尚于两汉班马唐宋八家。然从今细察。则未尝全无可议。如东坡醉白堂记。荆公以为韩白优劣论。介甫袁州学记。子瞻以为学校策。又如枯枝流芥。佛头着粪。固多有说。评品之高。至曰晋无唐无。则文字得失。文人诋诃。自来难平如此。而至于儒贤文字。尤皆平铺。难以业文家法绳划。然其用不用则又不系于此。必待无可议而用。则古今文可刻者无几。虽程朱子。盖或难矣。孔子尝称郑之辞命之美。然四手非谓常有。又未必邦国皆有此四手。则凡辞命固未必皆美而无可议也。美则不如。可议则不无。安知以是为可用不可用之决耶。如张子正蒙。岂非妙契之书。而程子乃曰子厚过处在正蒙。程子易传。是七十未传之书。而至朱子于义理文义。议其差误处。多不胜纪。则斯二书者。亦非为无可议之文而以此废之。不刊不用。则亦未曾闻也。春秋有断烂之毁。马史有草本之疑。行者未尝无议。议者未必不行。如明道志。固非无憾。尤翁言之。而栗谷墓碑。亦将谓无可议而得行耶。且虽孔子。于文辞则有可与人共者。况八九十岁笃老人文字。无怪其宲容有可禀
有宗旨。文字得失。本不足为碑之可刻不可刻之断案。夫后世称文章。莫尚于两汉班马唐宋八家。然从今细察。则未尝全无可议。如东坡醉白堂记。荆公以为韩白优劣论。介甫袁州学记。子瞻以为学校策。又如枯枝流芥。佛头着粪。固多有说。评品之高。至曰晋无唐无。则文字得失。文人诋诃。自来难平如此。而至于儒贤文字。尤皆平铺。难以业文家法绳划。然其用不用则又不系于此。必待无可议而用。则古今文可刻者无几。虽程朱子。盖或难矣。孔子尝称郑之辞命之美。然四手非谓常有。又未必邦国皆有此四手。则凡辞命固未必皆美而无可议也。美则不如。可议则不无。安知以是为可用不可用之决耶。如张子正蒙。岂非妙契之书。而程子乃曰子厚过处在正蒙。程子易传。是七十未传之书。而至朱子于义理文义。议其差误处。多不胜纪。则斯二书者。亦非为无可议之文而以此废之。不刊不用。则亦未曾闻也。春秋有断烂之毁。马史有草本之疑。行者未尝无议。议者未必不行。如明道志。固非无憾。尤翁言之。而栗谷墓碑。亦将谓无可议而得行耶。且虽孔子。于文辞则有可与人共者。况八九十岁笃老人文字。无怪其宲容有可禀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3H 页
 质者。而既未参听于当时。今无可及。此为深恨。然孔子曰辞达而已。今其为文事。实无缺。则顾不可拟于辞达。而必可作覆瓿之太玄耶。且此院移建。继 皇庙之后。则固春秋之义重矣。抑先生半世杖屦藏修之地。非同祭之义。则卒可无妥侑之义耶。故庙未建之前。固已先有院享矣。况春秋之义虽大。在尤翁。却是全体之一端。敦化中川流。而并其庙议出于尤翁制作之末光。(尤翁八十三年道德事功。皆在 皇庙之前。而皇庙之义。只是耽罗以后始语及者。)则此碑事体视庙碑。岂不又有间乎。今其序铭中皆已及春秋之义。则其分数之充尽与否。固非眼无文衡者所可与知。若如盛教。必不容他辞而一主于此。从头至尾。一则春秋。二则春秋。直成一个春秋碑然后。文可刻而碑可树。则亦恐分数之过占而无惑。反为春秋所乱乎。至于理气云云。苟其义无差。不言古不必为不可用。言之安知其必不可用耶。紫云之例。固先师所窃取。然窃取者。犹自道也。颜渊曰舜何人。予何人。祖营曰文章须自出机杼。何能共人生活。若使其例无害。起亦可也。又何必取尤翁起例于紫云。而先师亦可起例于华阳。则其以事例之同为准者。又安知必为究极之理耶。故理气说之可有可无。
质者。而既未参听于当时。今无可及。此为深恨。然孔子曰辞达而已。今其为文事。实无缺。则顾不可拟于辞达。而必可作覆瓿之太玄耶。且此院移建。继 皇庙之后。则固春秋之义重矣。抑先生半世杖屦藏修之地。非同祭之义。则卒可无妥侑之义耶。故庙未建之前。固已先有院享矣。况春秋之义虽大。在尤翁。却是全体之一端。敦化中川流。而并其庙议出于尤翁制作之末光。(尤翁八十三年道德事功。皆在 皇庙之前。而皇庙之义。只是耽罗以后始语及者。)则此碑事体视庙碑。岂不又有间乎。今其序铭中皆已及春秋之义。则其分数之充尽与否。固非眼无文衡者所可与知。若如盛教。必不容他辞而一主于此。从头至尾。一则春秋。二则春秋。直成一个春秋碑然后。文可刻而碑可树。则亦恐分数之过占而无惑。反为春秋所乱乎。至于理气云云。苟其义无差。不言古不必为不可用。言之安知其必不可用耶。紫云之例。固先师所窃取。然窃取者。犹自道也。颜渊曰舜何人。予何人。祖营曰文章须自出机杼。何能共人生活。若使其例无害。起亦可也。又何必取尤翁起例于紫云。而先师亦可起例于华阳。则其以事例之同为准者。又安知必为究极之理耶。故理气说之可有可无。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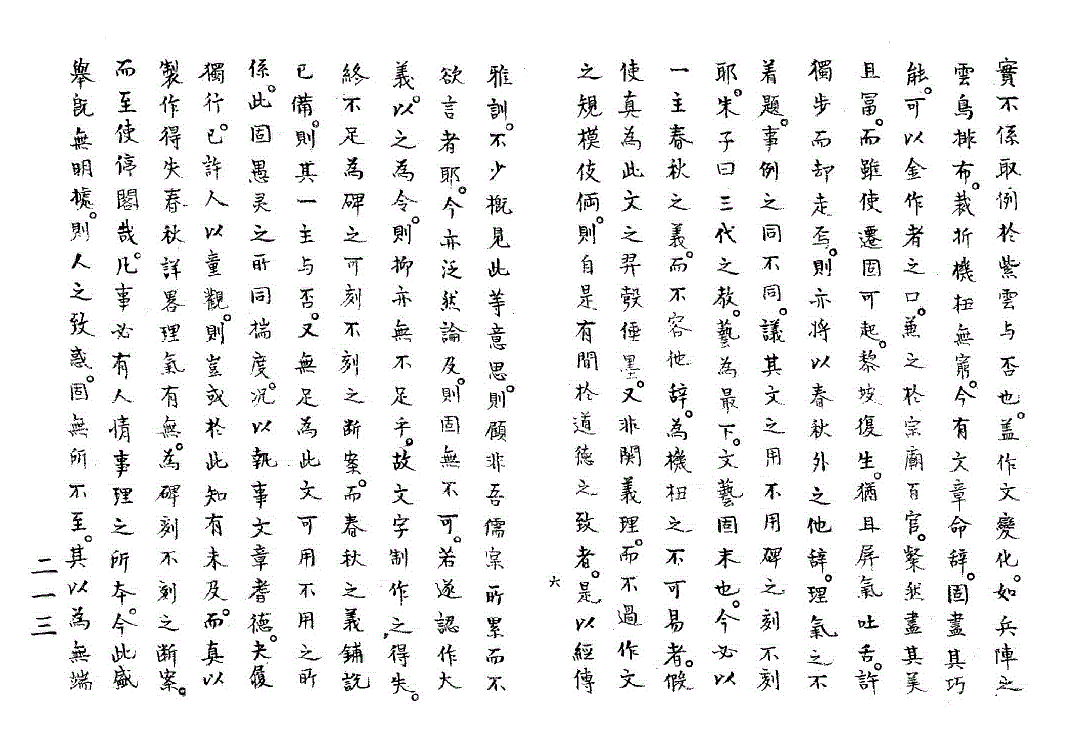 实不系取例于紫云与否也。盖作文变化。如兵阵之云鸟排布。裁折机杻无穷。今有文章命辞。固尽其巧能。可以金作者之口。兼之于宗庙百官。粲然尽其美且富。而虽使迁固可起。黎坡复生。犹且屏气吐舌。许独步而却走焉。则亦将以春秋外之他辞。理气之不着题。事例之同不同。议其文之用不用碑之刻不刻耶。朱子曰三代之教。艺为最下。文艺固末也。今必以一主春秋之义。而不容他辞。为机杻之不可易者。假使真为此文之羿彀倕墨。又非关义理。而不过作文之规模伎俩。则自是有间于道德之致者。是以经传雅训。不少概见此等意思。则顾非吾儒宲所累而不欲言者耶。今亦泛然论及。则固无不可。若遂认作大义。以之为令。则抑亦无不足乎。故文字制作之得失。终不足为碑之可刻不刻之断案。而春秋之义铺说已备。则其一主与否。又无足为此文可用不用之所系。此固愚灵之所同揣度。况以执事文章耆德。夬履独行。已许人以童观。则岂或于此知有未及。而真以制作得失春秋详略理气有无。为碑刻不刻之断案。而至使停阁哉。凡事必有人情事理之所本。今此盛举既无明据。则人之致惑。固无所不至。其以为无端
实不系取例于紫云与否也。盖作文变化。如兵阵之云鸟排布。裁折机杻无穷。今有文章命辞。固尽其巧能。可以金作者之口。兼之于宗庙百官。粲然尽其美且富。而虽使迁固可起。黎坡复生。犹且屏气吐舌。许独步而却走焉。则亦将以春秋外之他辞。理气之不着题。事例之同不同。议其文之用不用碑之刻不刻耶。朱子曰三代之教。艺为最下。文艺固末也。今必以一主春秋之义。而不容他辞。为机杻之不可易者。假使真为此文之羿彀倕墨。又非关义理。而不过作文之规模伎俩。则自是有间于道德之致者。是以经传雅训。不少概见此等意思。则顾非吾儒宲所累而不欲言者耶。今亦泛然论及。则固无不可。若遂认作大义。以之为令。则抑亦无不足乎。故文字制作之得失。终不足为碑之可刻不刻之断案。而春秋之义铺说已备。则其一主与否。又无足为此文可用不用之所系。此固愚灵之所同揣度。况以执事文章耆德。夬履独行。已许人以童观。则岂或于此知有未及。而真以制作得失春秋详略理气有无。为碑刻不刻之断案。而至使停阁哉。凡事必有人情事理之所本。今此盛举既无明据。则人之致惑。固无所不至。其以为无端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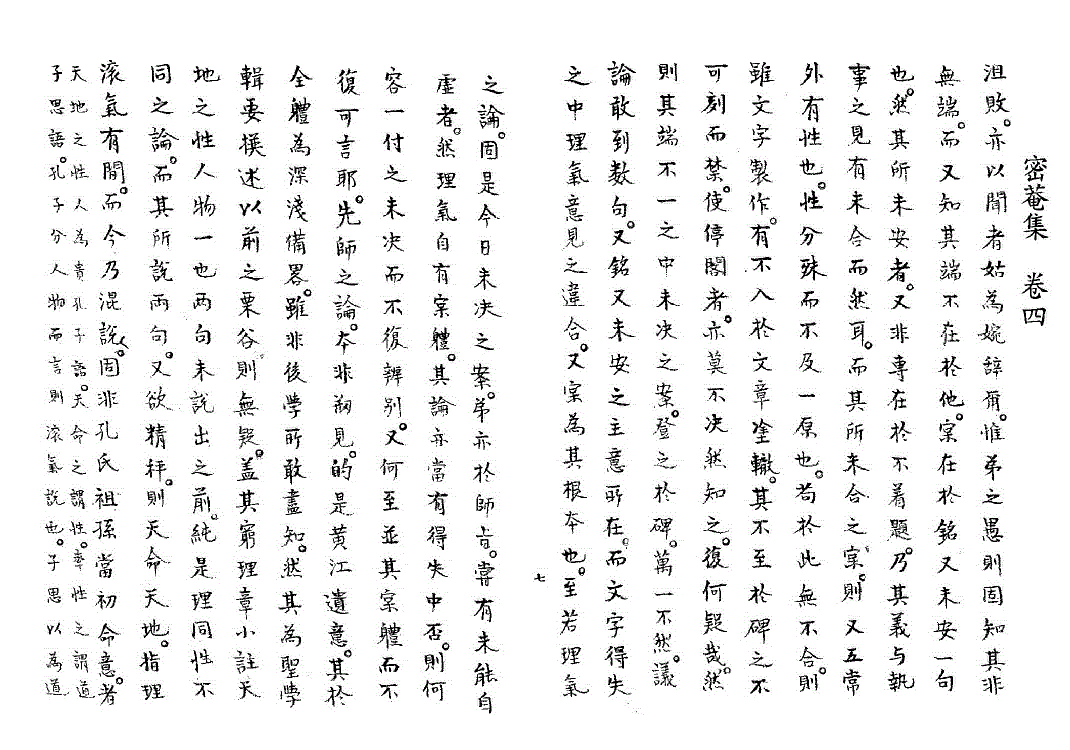 沮败。亦以闻者姑为婉辞尔。惟弟之愚则固知其非无端。而又知其端不在于他。宲在于铭又未安一句也。然其所未安者。又非专在于不着题。乃其义与执事之见有未合而然耳。而其所未合之宲。则又五常外有性也。性分殊而不及一原也。苟于此无不合。则虽文字制作。有不入于文章涂辙。其不至于碑之不可刻而禁。使停阁者。亦莫不决然知之。复何疑哉。然则其端不一之中未决之案。登之于碑。万一不然。议论敢到数句。又铭又未安之主意所在。而文字得失之中理气意见之违合。又宲为其根本也。至若理气之论。固是今日未决之案。弟亦于师旨。尝有未能自虚者。然理气自有宲体。其论亦当有得失中否。则何容一付之未决而不复辨别。又何至并其宲体而不复可言耶。先师之论。本非刱见。的是黄江遗意。其于全体为深浅备略。虽非后学所敢尽知。然其为圣学辑要撰述以前之栗谷则无疑。盖其穷理章小注天地之性人物一也两句未说出之前。纯是理同性不同之论。而其所说两句。又欲精秤。则天命天地。指理滚气有间。而今乃混说者。固非孔氏祖孙当初命意。(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子思语。孔子分人物而言则滚气说也。子思以为道
沮败。亦以闻者姑为婉辞尔。惟弟之愚则固知其非无端。而又知其端不在于他。宲在于铭又未安一句也。然其所未安者。又非专在于不着题。乃其义与执事之见有未合而然耳。而其所未合之宲。则又五常外有性也。性分殊而不及一原也。苟于此无不合。则虽文字制作。有不入于文章涂辙。其不至于碑之不可刻而禁。使停阁者。亦莫不决然知之。复何疑哉。然则其端不一之中未决之案。登之于碑。万一不然。议论敢到数句。又铭又未安之主意所在。而文字得失之中理气意见之违合。又宲为其根本也。至若理气之论。固是今日未决之案。弟亦于师旨。尝有未能自虚者。然理气自有宲体。其论亦当有得失中否。则何容一付之未决而不复辨别。又何至并其宲体而不复可言耶。先师之论。本非刱见。的是黄江遗意。其于全体为深浅备略。虽非后学所敢尽知。然其为圣学辑要撰述以前之栗谷则无疑。盖其穷理章小注天地之性人物一也两句未说出之前。纯是理同性不同之论。而其所说两句。又欲精秤。则天命天地。指理滚气有间。而今乃混说者。固非孔氏祖孙当初命意。(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子思语。孔子分人物而言则滚气说也。子思以为道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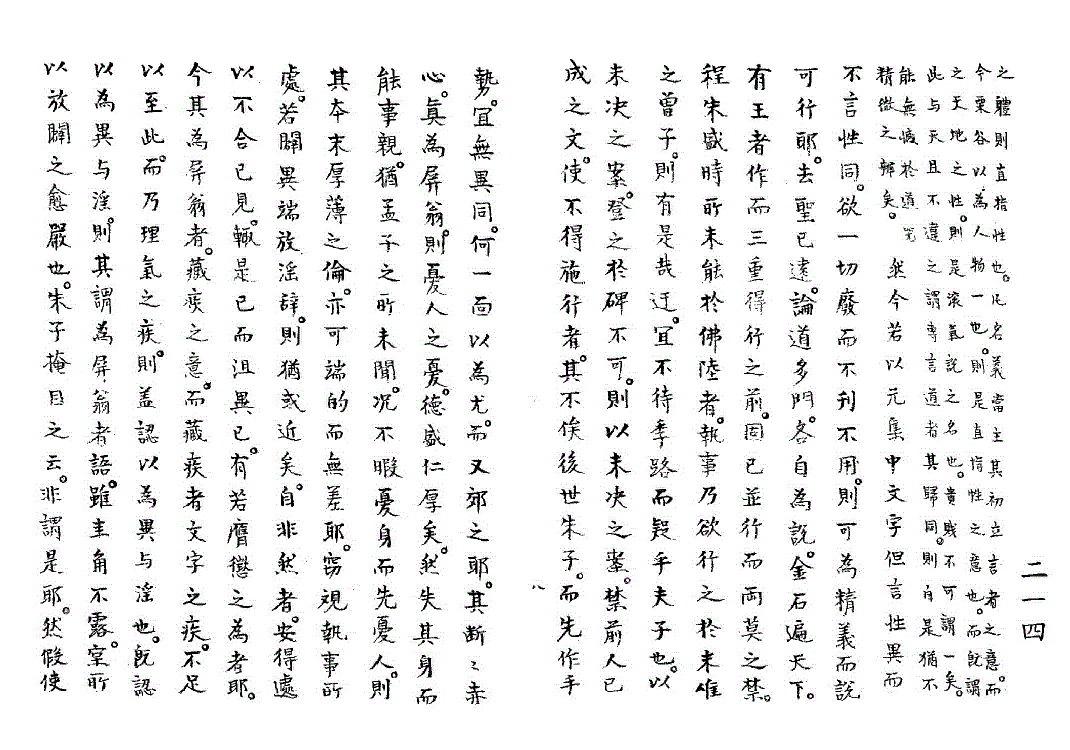 之体则直指性也。凡名义当主其初立言者之意。而今栗谷以为人物一也。则是直指性之意也。而既谓之天地之性。则是滚气说之名也。贵贱不可谓一矣。此与天且不违之谓专言道者其归同。则自是犹不能无憾于道器精微之辨矣。)然今若以元集中文字但言性异而不言性同。欲一切废而不刊不用。则可为精义而说可行耶。去圣已远。论道多门。各自为说。金石遍天下。有王者作而三重得行之前。固已并行而两莫之禁。程朱盛时所未能于佛陆者。执事乃欲行之于未唯之曾子。则有是哉迂。宜不待季路而疑乎夫子也。以未决之案。登之于碑不可。则以未决之案。禁前人已成之文。使不得施行者。其不俟后世朱子。而先作手势。宜无异同。何一面以为尤。而又郊之耶。其断断赤心。真为屏翁。则忧人之忧。德盛仁厚矣。然失其身而能事亲。犹孟子之所未闻。况不暇忧身而先忧人。则其本末厚薄之伦。亦可端的而无差耶。窃观执事所处。若辟异端放淫辞。则犹或近矣。自非然者。安得遽以不合己见。辄是己而沮异己。有若膺惩之为者耶。今其为屏翁者。藏疾之意。而藏疾者文字之疾。不足以至此。而乃理气之疾。则盖认以为异与淫也。既认以为异与淫。则其谓为屏翁者语。虽圭角不露。宲所以放辟之愈严也。朱子掩目之云。非谓是耶。然假使
之体则直指性也。凡名义当主其初立言者之意。而今栗谷以为人物一也。则是直指性之意也。而既谓之天地之性。则是滚气说之名也。贵贱不可谓一矣。此与天且不违之谓专言道者其归同。则自是犹不能无憾于道器精微之辨矣。)然今若以元集中文字但言性异而不言性同。欲一切废而不刊不用。则可为精义而说可行耶。去圣已远。论道多门。各自为说。金石遍天下。有王者作而三重得行之前。固已并行而两莫之禁。程朱盛时所未能于佛陆者。执事乃欲行之于未唯之曾子。则有是哉迂。宜不待季路而疑乎夫子也。以未决之案。登之于碑不可。则以未决之案。禁前人已成之文。使不得施行者。其不俟后世朱子。而先作手势。宜无异同。何一面以为尤。而又郊之耶。其断断赤心。真为屏翁。则忧人之忧。德盛仁厚矣。然失其身而能事亲。犹孟子之所未闻。况不暇忧身而先忧人。则其本末厚薄之伦。亦可端的而无差耶。窃观执事所处。若辟异端放淫辞。则犹或近矣。自非然者。安得遽以不合己见。辄是己而沮异己。有若膺惩之为者耶。今其为屏翁者。藏疾之意。而藏疾者文字之疾。不足以至此。而乃理气之疾。则盖认以为异与淫也。既认以为异与淫。则其谓为屏翁者语。虽圭角不露。宲所以放辟之愈严也。朱子掩目之云。非谓是耶。然假使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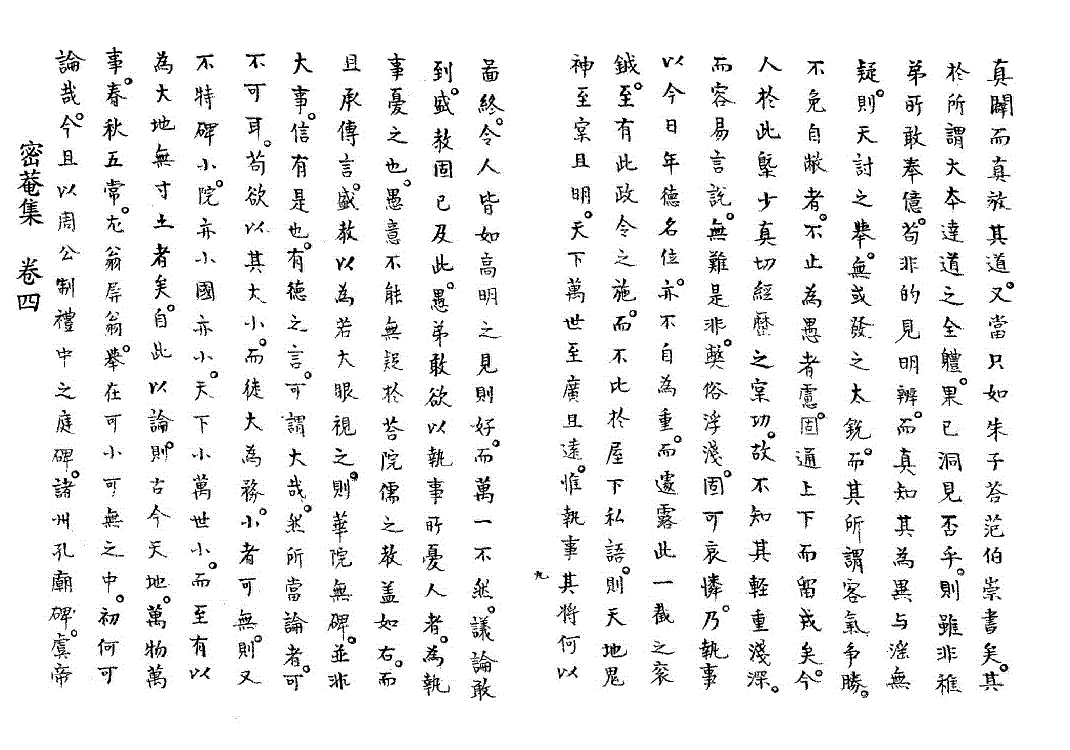 真辟而真放其道。又当只如朱子答范伯崇书矣。其于所谓大本达道之全体。果已洞见否乎。则虽非稚弟所敢奉亿。苟非的见明辨。而真知其为异与淫无疑。则天讨之举。无或发之太锐。而其所谓客气争胜。不免自敝者。不止为愚者虑。固通上下而留戒矣。今人于此槩少真切经历之宲功。故不知其轻重浅深。而容易言说。无难是非。弊俗浮浅。固可哀怜。乃执事以今日年德名位。亦不自为重。而遽露此一截之衮钺。至有此政令之施。而不比于屋下私语。则天地鬼神至宲且明。天下万世至广且远。惟执事其将何以啚终。令人皆如高明之见则好。而万一不然。议论敢到。盛教固已及此。愚弟敢欲以执事所忧人者。为执事忧之也。愚意不能无疑于答院儒之教盖如右。而且承传言。盛教以为若大眼视之。则华院无碑。并非大事。信有是也。有德之言。可谓大哉。然所当论者。可不可耳。苟欲以其大小。而徒大为务。小者可无。则又不特碑小。院亦小国亦小。天下小万世小。而至有以为大地无寸土者矣。自此以论。则古今天地。万物万事。春秋五常。尤翁屏翁。举在可小可无之中。初何可论哉。今且以周公制礼中之庭碑。诸州孔庙碑。虞帝
真辟而真放其道。又当只如朱子答范伯崇书矣。其于所谓大本达道之全体。果已洞见否乎。则虽非稚弟所敢奉亿。苟非的见明辨。而真知其为异与淫无疑。则天讨之举。无或发之太锐。而其所谓客气争胜。不免自敝者。不止为愚者虑。固通上下而留戒矣。今人于此槩少真切经历之宲功。故不知其轻重浅深。而容易言说。无难是非。弊俗浮浅。固可哀怜。乃执事以今日年德名位。亦不自为重。而遽露此一截之衮钺。至有此政令之施。而不比于屋下私语。则天地鬼神至宲且明。天下万世至广且远。惟执事其将何以啚终。令人皆如高明之见则好。而万一不然。议论敢到。盛教固已及此。愚弟敢欲以执事所忧人者。为执事忧之也。愚意不能无疑于答院儒之教盖如右。而且承传言。盛教以为若大眼视之。则华院无碑。并非大事。信有是也。有德之言。可谓大哉。然所当论者。可不可耳。苟欲以其大小。而徒大为务。小者可无。则又不特碑小。院亦小国亦小。天下小万世小。而至有以为大地无寸土者矣。自此以论。则古今天地。万物万事。春秋五常。尤翁屏翁。举在可小可无之中。初何可论哉。今且以周公制礼中之庭碑。诸州孔庙碑。虞帝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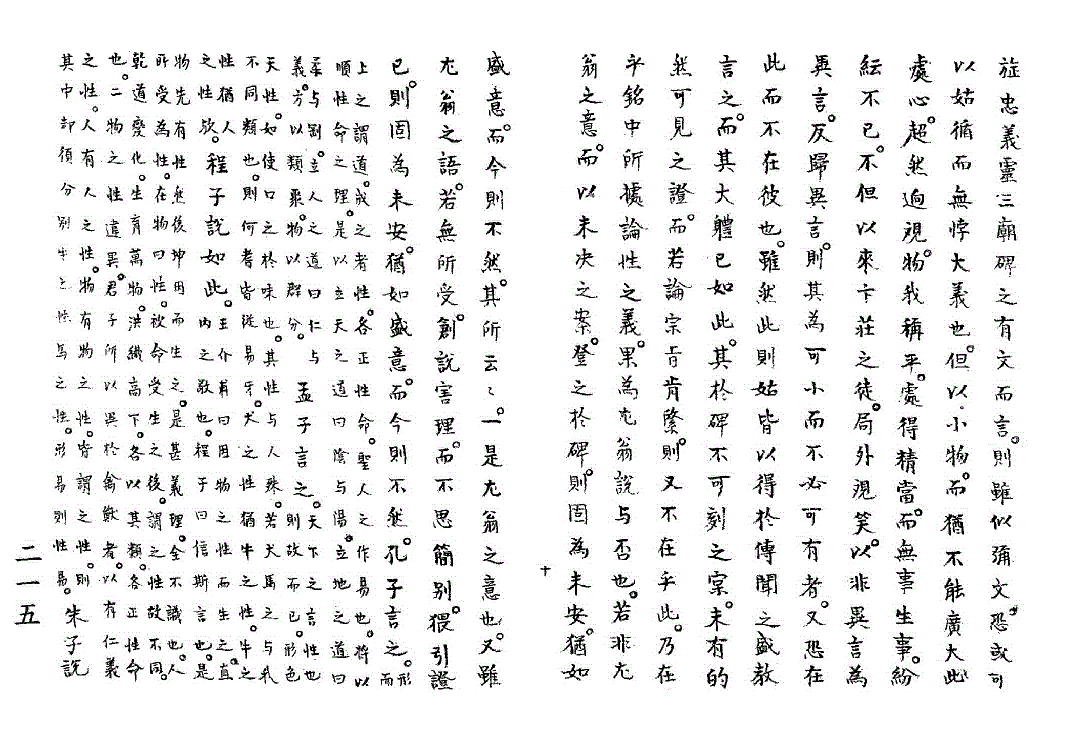 旌忠义灵三庙碑之有文而言。则虽似弥文。恐或可以姑循而无悖大义也。但以小物。而犹不能广大此处心。超然迥观。物我称平。处得精当。而无事生事。纷纭不已。不但以来卞庄之徒。局外观笑。以非异言为异言。反归异言。则其为可小而不必可有者。又恐在此而不在彼也。虽然此则姑皆以得于传闻之盛教言之。而其大体已如此。其于碑不可刻之宲。未有的然可见之證。而若论宗旨肯綮。则又不在乎此。乃在乎铭中所据论性之义。果为尤翁说与否也。若非尤翁之意。而以未决之案。登之于碑。则固为未安。犹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其所云云。一是尤翁之意也。又虽尤翁之语。若无所受。创说害理。而不思简别。猥引證已。则固为未安。犹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孔子言之。(形而上之谓道。成之者性。各正性命。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孟子言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形色天性。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何耆皆从易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程子说如此。(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内之敬也。程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后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人所受为性。在物曰性。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故不同。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二物之性违异。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皆谓之性。则其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形易则性易。)朱子说
旌忠义灵三庙碑之有文而言。则虽似弥文。恐或可以姑循而无悖大义也。但以小物。而犹不能广大此处心。超然迥观。物我称平。处得精当。而无事生事。纷纭不已。不但以来卞庄之徒。局外观笑。以非异言为异言。反归异言。则其为可小而不必可有者。又恐在此而不在彼也。虽然此则姑皆以得于传闻之盛教言之。而其大体已如此。其于碑不可刻之宲。未有的然可见之證。而若论宗旨肯綮。则又不在乎此。乃在乎铭中所据论性之义。果为尤翁说与否也。若非尤翁之意。而以未决之案。登之于碑。则固为未安。犹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其所云云。一是尤翁之意也。又虽尤翁之语。若无所受。创说害理。而不思简别。猥引證已。则固为未安。犹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孔子言之。(形而上之谓道。成之者性。各正性命。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孟子言之。(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形色天性。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何耆皆从易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程子说如此。(王介甫曰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内之敬也。程子曰信斯言也。是物先有性然后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人所受为性。在物曰性。被命受生之后。谓之性故不同。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二物之性违异。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皆谓之性。则其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形易则性易。)朱子说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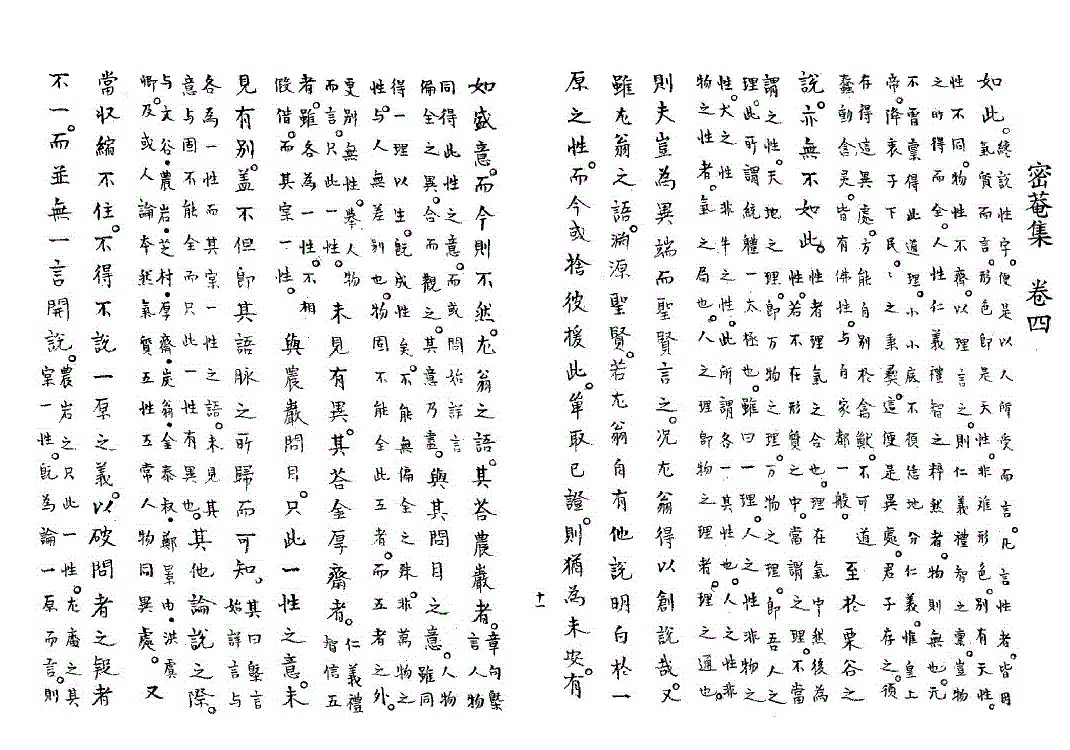 如此。(才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形色即是天性。非离形色。别有天性。性不同。物性不齐。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人性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元不曾禀得此道理。小小底不须恁地分仁义。惟皇上帝。降衷子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君子存之。须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都一般。)至于栗谷之说。亦无不如此。(性者理气之合也。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天地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之理。即吾人之理。此所谓统体一太极也。虽曰一理。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谓各一其性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气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则夫岂为异端而圣贤言之。况尤翁得以创说哉。又虽尤翁之语。渊源圣贤。若尤翁自有他说明白于一原之性。而今或舍彼援此。单取已證。则犹为未安。有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尤翁之语。其答农岩者。(章句槩言人物同得此性之意。而或问始详言偏全之异。合而观之。其意乃尽。)与其问目之意。(人物虽同得一理以生。既成性矣。不能无偏全之殊。非万物之性。与人无差别也。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别无性。举人物而言。只此一性。)未见有异。其答金厚斋者。(仁义礼智信五者。虽各为一性。不相假借。而其宲一性。)与农岩问目。只此一性之意。未见有别。盖不但即其语脉之所归而可知。(其曰槩言始详言与各为一性而其宲一性之语。未见其意与固不能全而只此一性有异也)其他论说之际。(与文谷,农岩,芝村,厚斋,炭翁,金泰叔,郑景由,洪虞卿。及或人论本然气质五性五常人物同异处。)又当收缩不住。不得不说一原之义。以破问者之疑者不一。而并无一言开说。(农岩之只此一性。尤庵之其宲一性。既为论一原而言。则
如此。(才说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言。形色即是天性。非离形色。别有天性。性不同。物性不齐。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人性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元不曾禀得此道理。小小底不须恁地分仁义。惟皇上帝。降衷子下民。民之秉彝。这便是异处。君子存之。须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都一般。)至于栗谷之说。亦无不如此。(性者理气之合也。理在气中然后为性。若不在形质之中。当谓之理。不当谓之性。天地之理。即万物之理。万物之理。即吾人之理。此所谓统体一太极也。虽曰一理。人之性非物之性。犬之性非牛之性。此所谓各一其性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气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则夫岂为异端而圣贤言之。况尤翁得以创说哉。又虽尤翁之语。渊源圣贤。若尤翁自有他说明白于一原之性。而今或舍彼援此。单取已證。则犹为未安。有如盛意。而今则不然。尤翁之语。其答农岩者。(章句槩言人物同得此性之意。而或问始详言偏全之异。合而观之。其意乃尽。)与其问目之意。(人物虽同得一理以生。既成性矣。不能无偏全之殊。非万物之性。与人无差别也。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别无性。举人物而言。只此一性。)未见有异。其答金厚斋者。(仁义礼智信五者。虽各为一性。不相假借。而其宲一性。)与农岩问目。只此一性之意。未见有别。盖不但即其语脉之所归而可知。(其曰槩言始详言与各为一性而其宲一性之语。未见其意与固不能全而只此一性有异也)其他论说之际。(与文谷,农岩,芝村,厚斋,炭翁,金泰叔,郑景由,洪虞卿。及或人论本然气质五性五常人物同异处。)又当收缩不住。不得不说一原之义。以破问者之疑者不一。而并无一言开说。(农岩之只此一性。尤庵之其宲一性。既为论一原而言。则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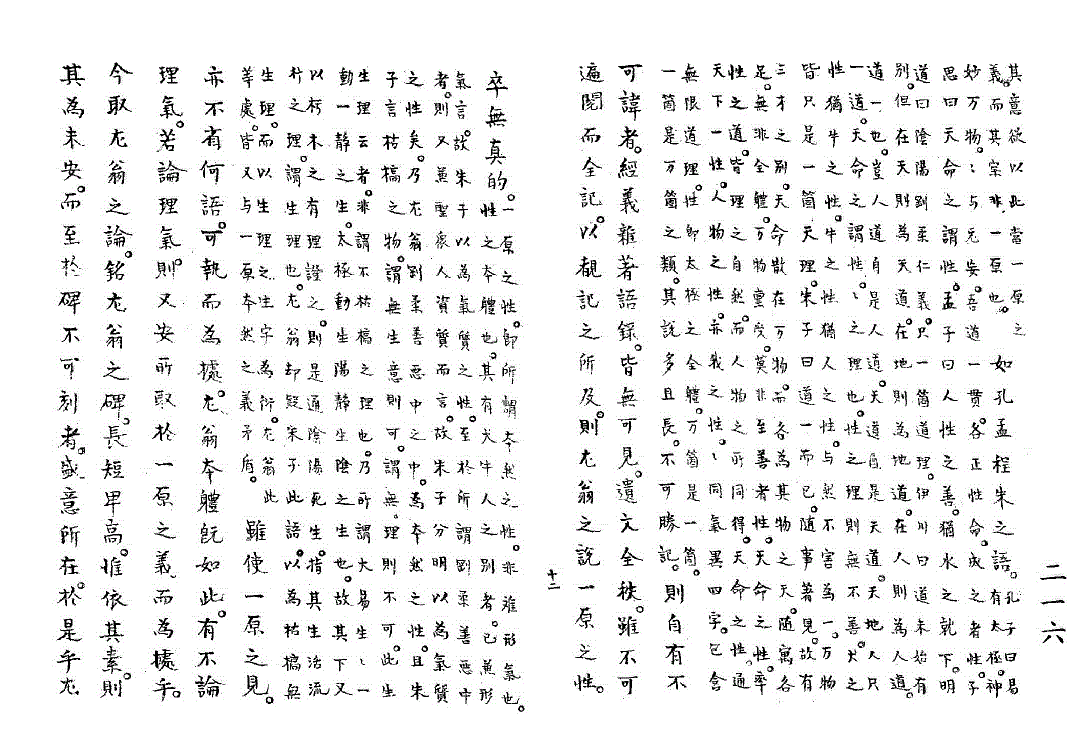 其意欲以此当一原之义。而其宲非一原也。)如孔孟程朱之语。(孔子曰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吾道一贯。各正性命。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明道曰阴阳刚柔仁义。只一个道理。伊川曰道未始有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天地人只一道。天命之谓性。性之理也。性之理则无不善。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朱子曰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随寓各足。无非全体。万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性同气异四字。包含无限道理。性即太极之全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之类。其说多且长。不可胜记。)则自有不可讳者。经义杂著语录。皆无可见。遗文全秩。虽不可遍阅而全记。以睹记之所及。则尤翁之说一原之性。卒无真的。(一原之性。即所谓本然之性。非离形气也。性之本体也。其有犬牛人之别者。已兼形气言。故朱子以为气质之性。至于所谓刚柔善恶中者。则又兼圣众人资质而言。故朱子分明以为气质之性矣。乃尤翁刚柔善恶中之中。为本然之性。且朱子言枯槁之物。谓无生意则可。谓无生理则不可。此生理云者。非谓不枯槁之理也。乃所谓大易生生一动一静之生。太极动生阳静生阴之生也。故其下又以朽木之有理證之。则是通阴阳死生。指其生活流行之理。谓生理也。尤翁却疑朱子此语。以为枯槁无生理。而以生理之生字为衍。尤翁此等处。皆又与一原本然之义矛盾。)虽使一原之见。亦不省何语。可执而为据。尤翁本体既如此。有不论理气。若论理气。则又安所取于一原之义而为据乎。今取尤翁之论。铭尤翁之碑。长短卑高。惟依其素。则其为未安。而至于碑不可刻者。盛意所在。于是乎尤
其意欲以此当一原之义。而其宲非一原也。)如孔孟程朱之语。(孔子曰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吾道一贯。各正性命。成之者性。子思曰天命之谓性。孟子曰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明道曰阴阳刚柔仁义。只一个道理。伊川曰道未始有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天地人只一道。天命之谓性。性之理也。性之理则无不善。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朱子曰道一而已。随事著见。故有三才之别。天命散在万物。而各为其物之天。随寓各足。无非全体。万物禀受。莫非至善者性。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天命之性。通天下一性。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性同气异四字。包含无限道理。性即太极之全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之类。其说多且长。不可胜记。)则自有不可讳者。经义杂著语录。皆无可见。遗文全秩。虽不可遍阅而全记。以睹记之所及。则尤翁之说一原之性。卒无真的。(一原之性。即所谓本然之性。非离形气也。性之本体也。其有犬牛人之别者。已兼形气言。故朱子以为气质之性。至于所谓刚柔善恶中者。则又兼圣众人资质而言。故朱子分明以为气质之性矣。乃尤翁刚柔善恶中之中。为本然之性。且朱子言枯槁之物。谓无生意则可。谓无生理则不可。此生理云者。非谓不枯槁之理也。乃所谓大易生生一动一静之生。太极动生阳静生阴之生也。故其下又以朽木之有理證之。则是通阴阳死生。指其生活流行之理。谓生理也。尤翁却疑朱子此语。以为枯槁无生理。而以生理之生字为衍。尤翁此等处。皆又与一原本然之义矛盾。)虽使一原之见。亦不省何语。可执而为据。尤翁本体既如此。有不论理气。若论理气。则又安所取于一原之义而为据乎。今取尤翁之论。铭尤翁之碑。长短卑高。惟依其素。则其为未安。而至于碑不可刻者。盛意所在。于是乎尤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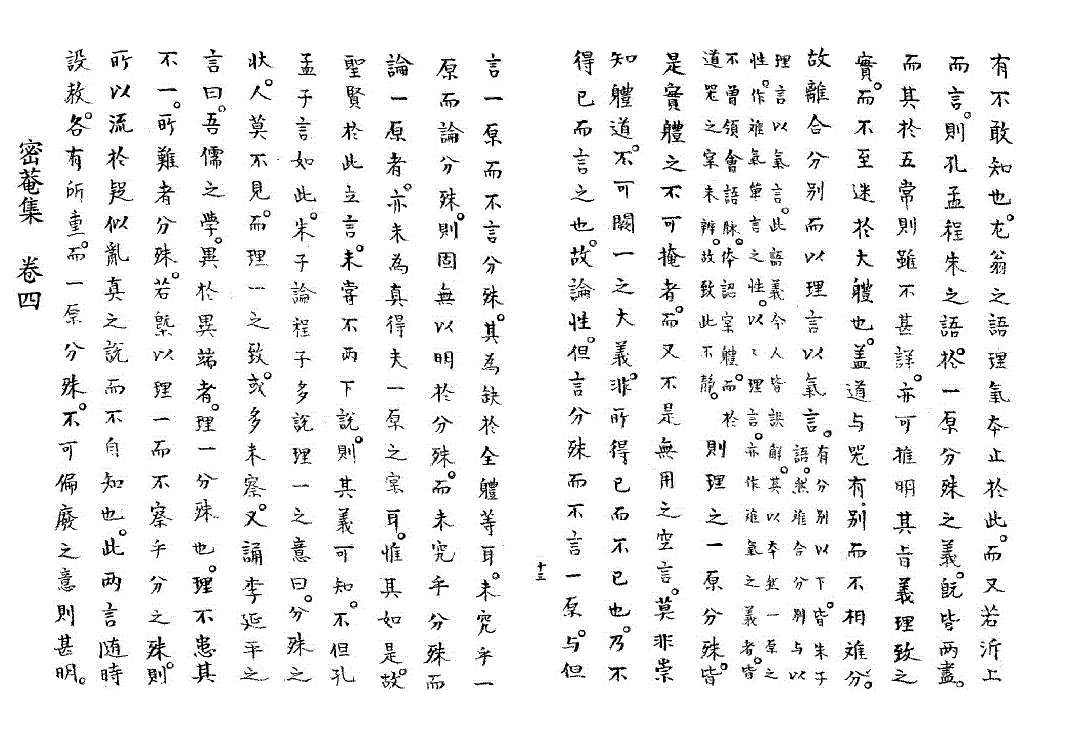 有不敢知也。尤翁之语理气本止于此。而又若溯上而言。则孔孟程朱之语。于一原分殊之义。既皆两尽。而其于五常则虽不甚详。亦可推明其旨义理致之实。而不至迷于大体也。盖道与器有分别而不相离。故离合分别而以理言以气言。(有分别以下。皆朱子语。然离合分别与以理言以气言。此语义今人皆误解。其以本然一原之性。作离气单言之性。以以理言。亦作离气之义者。皆不曾领会语脉。体认宲体。而于道器之宲未辨。故致此不静。)则理之一原分殊。皆是实体之不可掩者。而又不是无用之空言。莫非崇知体道。不可阙一之大义。非所得已而不已也。乃不得已而言之也。故论性。但言分殊而不言一原。与但言一原而不言分殊。其为缺于全体等耳。未究乎一原而论分殊。则固无以明于分殊。而未究乎分殊而论一原者。亦未为真得夫一原之宲耳。惟其如是。故圣贤于此立言。未尝不两下说。则其义可知。不但孔孟子言如此。朱子论程子多说理一之意曰。分殊之状。人莫不见。而理一之致。或多未察。又诵李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则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此两言随时设教。各有所重。而一原分殊。不可偏废之意则甚明。
有不敢知也。尤翁之语理气本止于此。而又若溯上而言。则孔孟程朱之语。于一原分殊之义。既皆两尽。而其于五常则虽不甚详。亦可推明其旨义理致之实。而不至迷于大体也。盖道与器有分别而不相离。故离合分别而以理言以气言。(有分别以下。皆朱子语。然离合分别与以理言以气言。此语义今人皆误解。其以本然一原之性。作离气单言之性。以以理言。亦作离气之义者。皆不曾领会语脉。体认宲体。而于道器之宲未辨。故致此不静。)则理之一原分殊。皆是实体之不可掩者。而又不是无用之空言。莫非崇知体道。不可阙一之大义。非所得已而不已也。乃不得已而言之也。故论性。但言分殊而不言一原。与但言一原而不言分殊。其为缺于全体等耳。未究乎一原而论分殊。则固无以明于分殊。而未究乎分殊而论一原者。亦未为真得夫一原之宲耳。惟其如是。故圣贤于此立言。未尝不两下说。则其义可知。不但孔孟子言如此。朱子论程子多说理一之意曰。分殊之状。人莫不见。而理一之致。或多未察。又诵李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则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此两言随时设教。各有所重。而一原分殊。不可偏废之意则甚明。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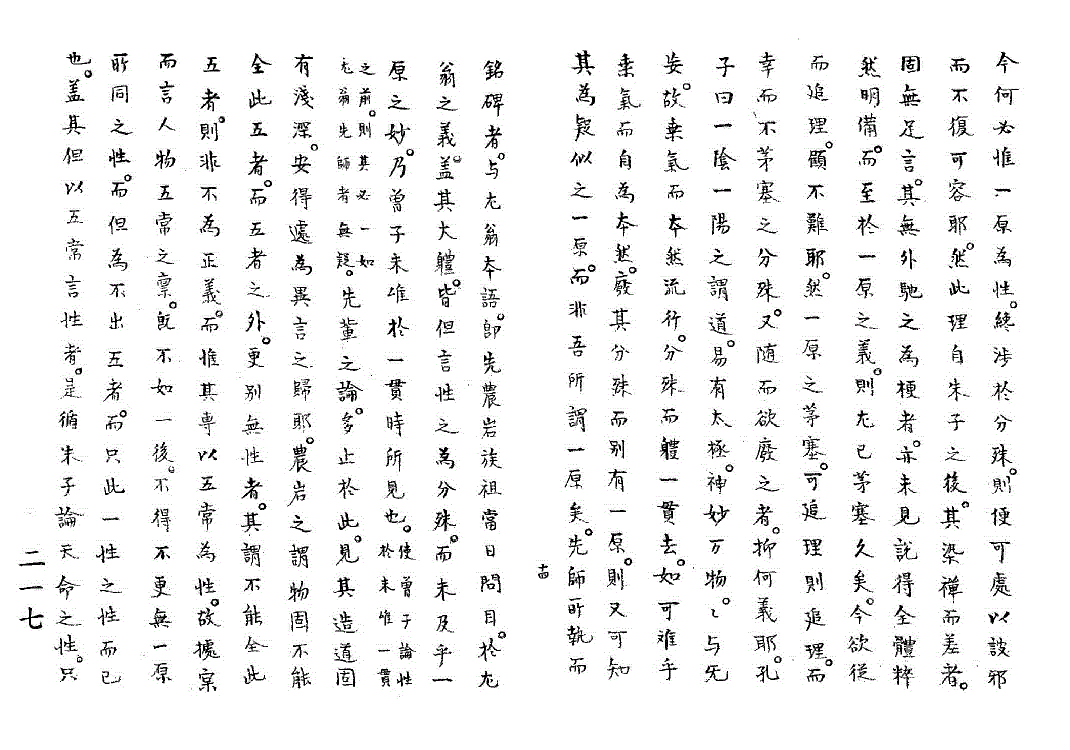 今何必惟一原为性。才涉于分殊。则便可处以诐邪而不复可容耶。然此理自朱子之后。其染禅而差者。固无足言。其无外驰之为梗者。亦未见说得全体粹然明备。而至于一原之义。则尤已茅塞久矣。今欲从而追理。顾不难耶。然一原之茅塞。可追理则追理。而幸而不茅塞之分殊。又随而欲废之者。抑何义耶。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故乘气而本然流行。分殊而体一贯去。如可离乎乘气而自为本然。废其分殊而别有一原。则又可知其为疑似之一原。而非吾所谓一原矣。先师所执而铭碑者。与尤翁本语。即先农岩族祖当日问目。于尤翁之义。盖其大体。皆但言性之为分殊。而未及乎一原之妙。乃曾子未唯于一贯时所见也。(使曾子论性于未唯一贯之前。则其必一如尤翁先师者无疑。)先辈之论。多止于此。见其造道固有浅深。安得遽为异言之归耶。农岩之谓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别无性者。其谓不能全此五者。则非不为正义。而惟其专以五常为性。故据宲而言人物五常之禀。既不如一后。不得不更无一原所同之性。而但为不出五者。而只此一性之性而已也。盖其但以五常言性者。是循朱子论天命之性。只
今何必惟一原为性。才涉于分殊。则便可处以诐邪而不复可容耶。然此理自朱子之后。其染禅而差者。固无足言。其无外驰之为梗者。亦未见说得全体粹然明备。而至于一原之义。则尤已茅塞久矣。今欲从而追理。顾不难耶。然一原之茅塞。可追理则追理。而幸而不茅塞之分殊。又随而欲废之者。抑何义耶。孔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故乘气而本然流行。分殊而体一贯去。如可离乎乘气而自为本然。废其分殊而别有一原。则又可知其为疑似之一原。而非吾所谓一原矣。先师所执而铭碑者。与尤翁本语。即先农岩族祖当日问目。于尤翁之义。盖其大体。皆但言性之为分殊。而未及乎一原之妙。乃曾子未唯于一贯时所见也。(使曾子论性于未唯一贯之前。则其必一如尤翁先师者无疑。)先辈之论。多止于此。见其造道固有浅深。安得遽为异言之归耶。农岩之谓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别无性者。其谓不能全此五者。则非不为正义。而惟其专以五常为性。故据宲而言人物五常之禀。既不如一后。不得不更无一原所同之性。而但为不出五者。而只此一性之性而已也。盖其但以五常言性者。是循朱子论天命之性。只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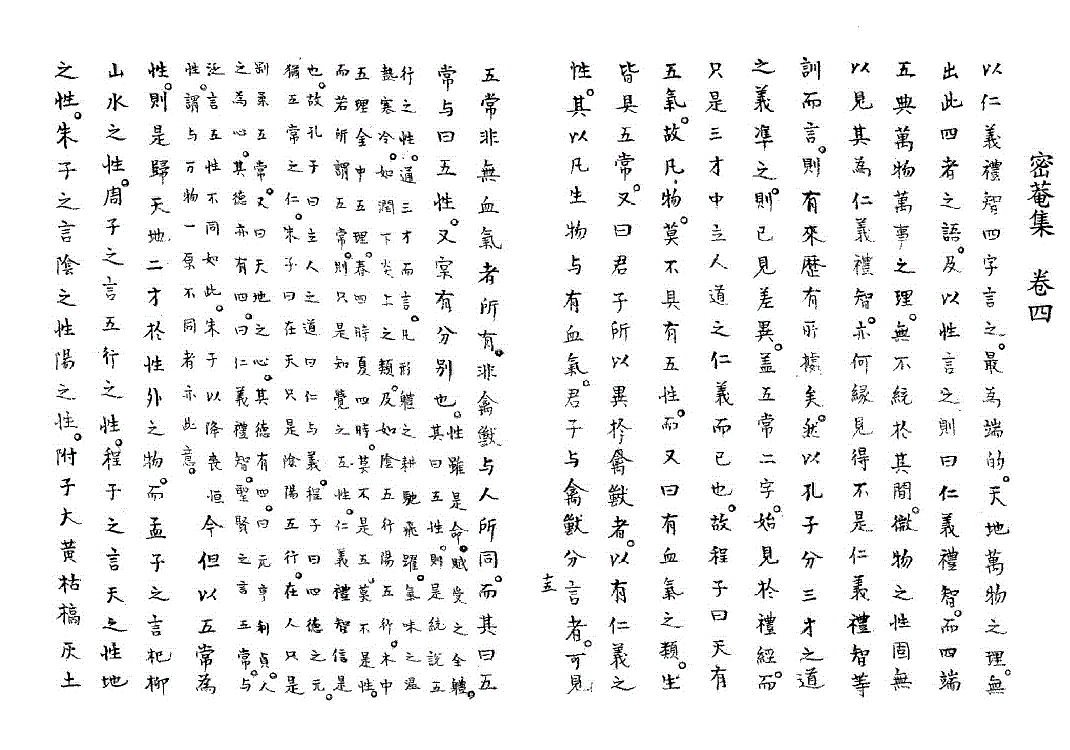 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天地万物之理。无出此四者之语。及以性言之则曰仁义礼智。而四端五典万物万事之理。无不统于其间。微物之性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等训而言。则有来历有所据矣。然以孔子分三才之道之义准之。则已见差异。盖五常二字。始见于礼经。而只是三才中立人道之仁义而已也。故程子曰天有五气。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而又曰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又曰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其以凡生物与有血气。君子与禽兽分言者。可见五常非无血气者所有。非禽兽与人所同。而其曰五常与曰五性。又宲有分别也。(性虽是命。赋受之全体。其曰五性。则是统说五行之性。通三才而言。凡形体之耕驰飞跃。气味之温热寒冷。如润下炎上之类。及如阴五行阳五行。木中五理金中五理。春四时夏四时。莫不是五。莫不是性。而若所谓五常。则只是知觉之五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故孔子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程子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朱子曰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只是刚柔五常。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圣贤之言五常。与泛言五性不同如此。朱子以降丧恒性。谓与万物一原不同者亦此意。)今但以五常为性。则是归天地二才于性外之物。而孟子之言杞柳山水之性。周子之言五行之性。程子之言天之性地之性。朱子之言阴之性阳之性。附子大黄枯槁灰土
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天地万物之理。无出此四者之语。及以性言之则曰仁义礼智。而四端五典万物万事之理。无不统于其间。微物之性固无以见其为仁义礼智。亦何缘见得不是仁义礼智等训而言。则有来历有所据矣。然以孔子分三才之道之义准之。则已见差异。盖五常二字。始见于礼经。而只是三才中立人道之仁义而已也。故程子曰天有五气。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而又曰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又曰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其以凡生物与有血气。君子与禽兽分言者。可见五常非无血气者所有。非禽兽与人所同。而其曰五常与曰五性。又宲有分别也。(性虽是命。赋受之全体。其曰五性。则是统说五行之性。通三才而言。凡形体之耕驰飞跃。气味之温热寒冷。如润下炎上之类。及如阴五行阳五行。木中五理金中五理。春四时夏四时。莫不是五。莫不是性。而若所谓五常。则只是知觉之五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故孔子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程子曰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朱子曰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只是刚柔五常。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圣贤之言五常。与泛言五性不同如此。朱子以降丧恒性。谓与万物一原不同者亦此意。)今但以五常为性。则是归天地二才于性外之物。而孟子之言杞柳山水之性。周子之言五行之性。程子之言天之性地之性。朱子之言阴之性阳之性。附子大黄枯槁灰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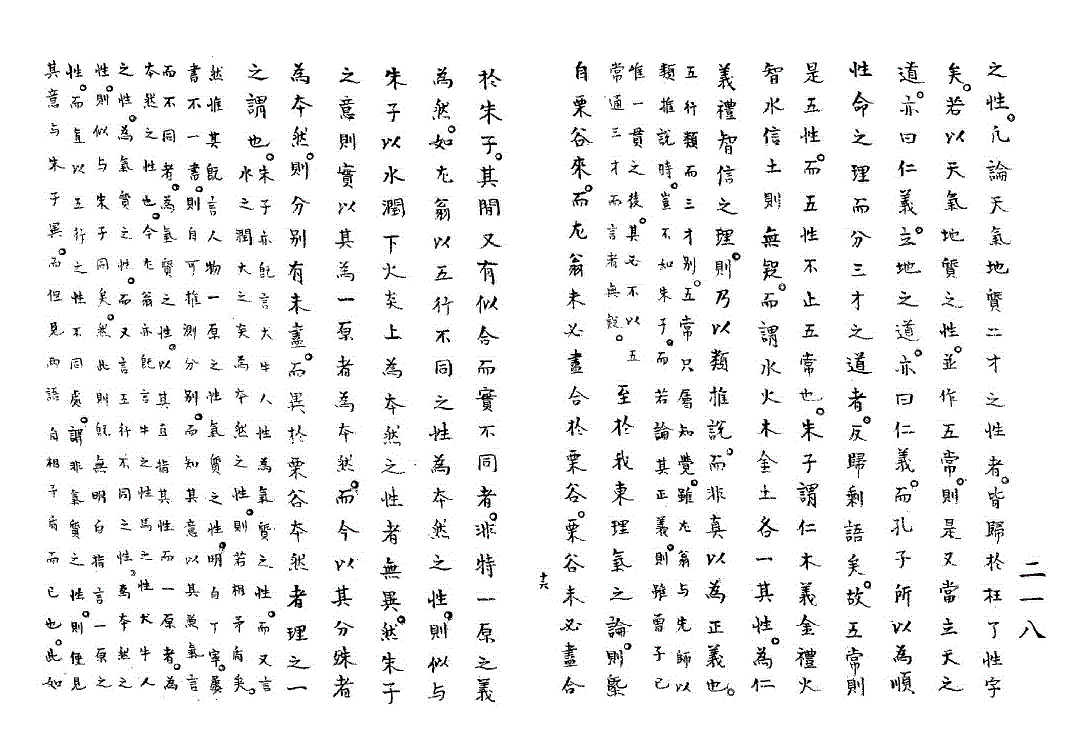 之性。凡论天气地质二才之性者。皆归于枉了性字矣。若以天气地质之性。并作五常。则是又当立天之道。亦曰仁义。立地之道。亦曰仁义。而孔子所以为顺性命之理而分三才之道者。反归剩语矣。故五常则是五性。而五性不止五常也。朱子谓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则无疑。而谓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理。则乃以类推说。而非真以为正义也。(五行类而三才别。五常只属知觉。虽尤翁与先师以类推说时。岂不如朱子。而若论其正义。则虽曾子已唯一贯之后。其必不以五常通三才而言者无疑。)至于我东理气之论。则槩自栗谷来。而尤翁未必尽合于栗谷。栗谷未必尽合于朱子。其间又有似合而实不同者。非特一原之义为然。如尤翁以五行不同之性为本然之性。则似与朱子以水润下火炎上为本然之性者无异。然朱子之意则实以其为一原者为本然。而今以其分殊者为本然。则分别有未尽。而异于栗谷本然者理之一之谓也。(朱子亦既言犬牛人性为气质之性。而又言水之润火之炎为本然之性。则若相矛盾矣。然惟其既言人物一原之性气质之性。明白丁宁。屡书不一书。则自可推测分别。而知其意以其兼气言而不同者。为气质之性。以其直指其性而一原者。为本然之性也。今尤翁亦既言牛之性马之性犬牛人之性。为气质之性。而又言五行不同之性。为本然之性。则似与朱子同矣。然此则既无明白指言一原之性。而直以五行之性不同处。谓非气质之性。则便见其意与朱子异。而但见两语自相矛盾而已也。此如
之性。凡论天气地质二才之性者。皆归于枉了性字矣。若以天气地质之性。并作五常。则是又当立天之道。亦曰仁义。立地之道。亦曰仁义。而孔子所以为顺性命之理而分三才之道者。反归剩语矣。故五常则是五性。而五性不止五常也。朱子谓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则无疑。而谓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理。则乃以类推说。而非真以为正义也。(五行类而三才别。五常只属知觉。虽尤翁与先师以类推说时。岂不如朱子。而若论其正义。则虽曾子已唯一贯之后。其必不以五常通三才而言者无疑。)至于我东理气之论。则槩自栗谷来。而尤翁未必尽合于栗谷。栗谷未必尽合于朱子。其间又有似合而实不同者。非特一原之义为然。如尤翁以五行不同之性为本然之性。则似与朱子以水润下火炎上为本然之性者无异。然朱子之意则实以其为一原者为本然。而今以其分殊者为本然。则分别有未尽。而异于栗谷本然者理之一之谓也。(朱子亦既言犬牛人性为气质之性。而又言水之润火之炎为本然之性。则若相矛盾矣。然惟其既言人物一原之性气质之性。明白丁宁。屡书不一书。则自可推测分别。而知其意以其兼气言而不同者。为气质之性。以其直指其性而一原者。为本然之性也。今尤翁亦既言牛之性马之性犬牛人之性。为气质之性。而又言五行不同之性。为本然之性。则似与朱子同矣。然此则既无明白指言一原之性。而直以五行之性不同处。谓非气质之性。则便见其意与朱子异。而但见两语自相矛盾而已也。此如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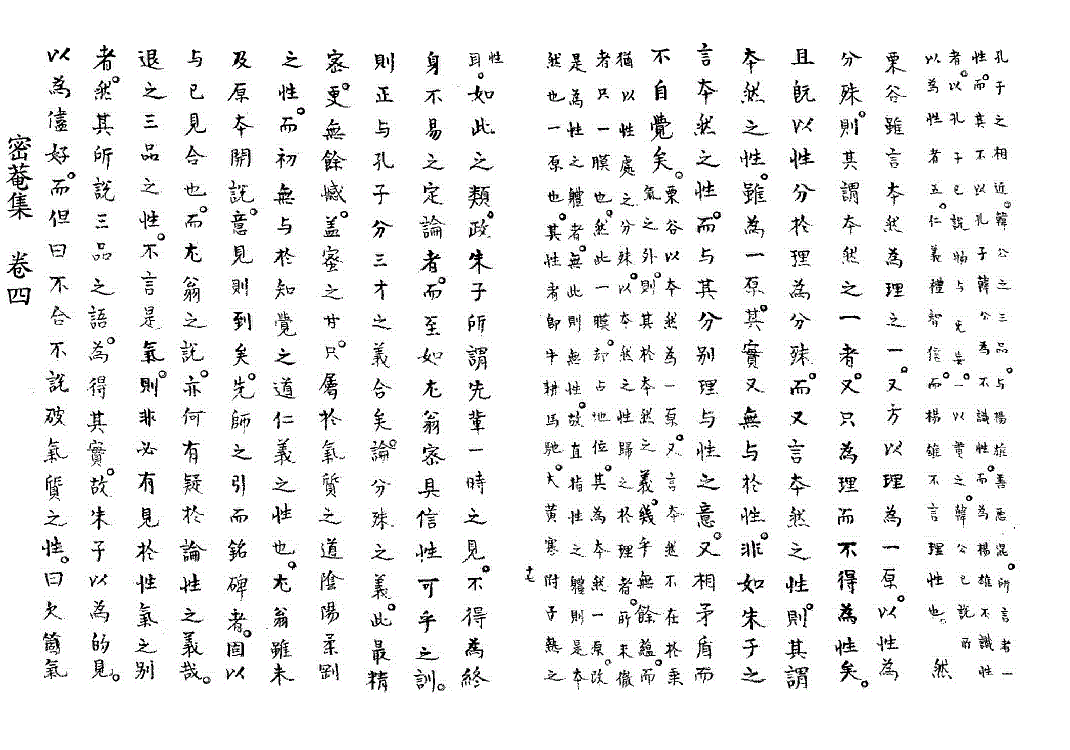 孔子之相近。韩公之三品。与杨雄善恶混。所言者一性。而其不以孔子韩公为不识性。而为杨雄不识性者。以孔子已说物与无妄。一以贯之。韩公已说所以为性者五。仁义礼智信。而杨雄不言理性也。)然栗谷虽言本然为理之一。又方以理为一原。以性为分殊。则其谓本然之一者。又只为理而不得为性矣。且既以性分于理为分殊。而又言本然之性。则其谓本然之性。虽为一原。其实又无与于性。非如朱子之言本然之性。而与其分别理与性之意。又相矛盾而不自觉矣。(栗谷以本然为一原。又言本然不在于乘气之外。则其于本然之义。几乎无馀蕴。而犹以性处之分殊。以本然之性归之于理者。所未彻者只一膜也。然此一膜。却占地位。其为本然一原。改是为性之体者。无此则无性。故直指性之体则是本然也一原也。其性者即牛耕马驰。大黄寒附子热之性耳。)如此之类。政朱子所谓先辈一时之见。不得为终身不易之定论者。而至如尤翁密具信性可乎之训。则正与孔子分三才之义合矣。论分殊之义。此最精密。更无馀憾。盖蜜之甘。只属于气质之道阴阳柔刚之性。而初无与于知觉之道仁义之性也。尤翁虽未及原本开说。意见则到矣。先师之引而铭碑者。固以与己见合也。而尤翁之说。亦何有疑于论性之义哉。退之三品之性。不言是气。则非必有见于性气之别者。然其所说三品之语。为得其实。故朱子以为的见。以为尽好。而但曰不合不说破气质之性。曰欠个气
孔子之相近。韩公之三品。与杨雄善恶混。所言者一性。而其不以孔子韩公为不识性。而为杨雄不识性者。以孔子已说物与无妄。一以贯之。韩公已说所以为性者五。仁义礼智信。而杨雄不言理性也。)然栗谷虽言本然为理之一。又方以理为一原。以性为分殊。则其谓本然之一者。又只为理而不得为性矣。且既以性分于理为分殊。而又言本然之性。则其谓本然之性。虽为一原。其实又无与于性。非如朱子之言本然之性。而与其分别理与性之意。又相矛盾而不自觉矣。(栗谷以本然为一原。又言本然不在于乘气之外。则其于本然之义。几乎无馀蕴。而犹以性处之分殊。以本然之性归之于理者。所未彻者只一膜也。然此一膜。却占地位。其为本然一原。改是为性之体者。无此则无性。故直指性之体则是本然也一原也。其性者即牛耕马驰。大黄寒附子热之性耳。)如此之类。政朱子所谓先辈一时之见。不得为终身不易之定论者。而至如尤翁密具信性可乎之训。则正与孔子分三才之义合矣。论分殊之义。此最精密。更无馀憾。盖蜜之甘。只属于气质之道阴阳柔刚之性。而初无与于知觉之道仁义之性也。尤翁虽未及原本开说。意见则到矣。先师之引而铭碑者。固以与己见合也。而尤翁之说。亦何有疑于论性之义哉。退之三品之性。不言是气。则非必有见于性气之别者。然其所说三品之语。为得其实。故朱子以为的见。以为尽好。而但曰不合不说破气质之性。曰欠个气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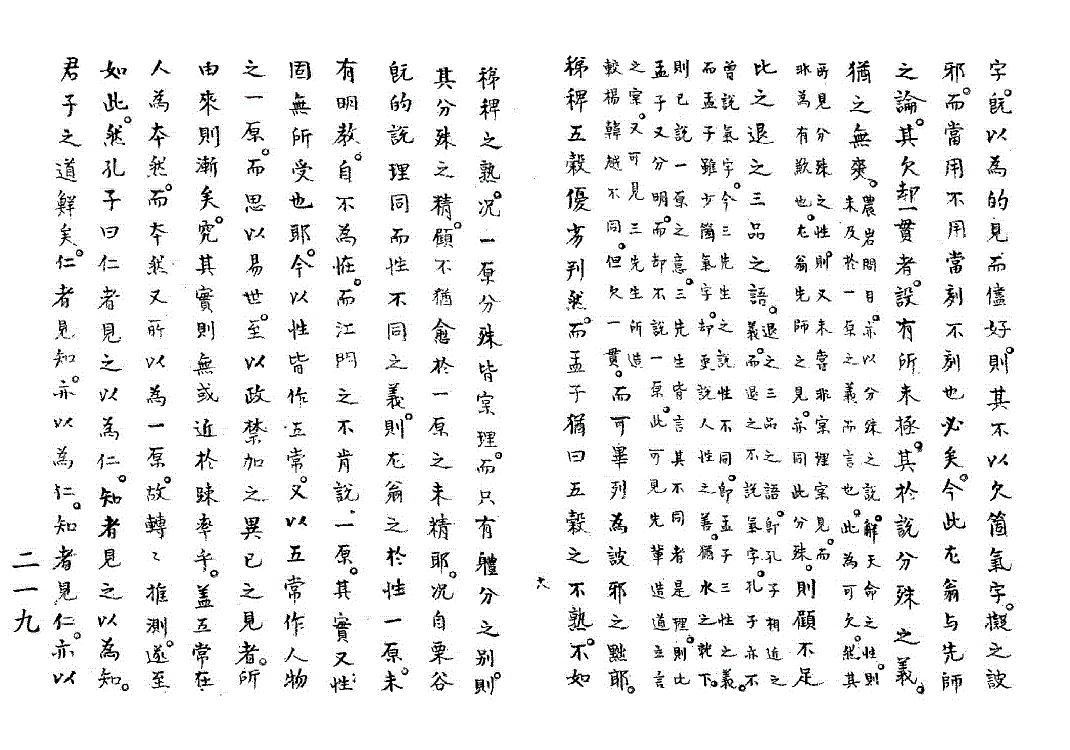 字。既以为的见而尽好。则其不以欠个气字。拟之诐邪。而当用不用当刻不刻也必矣。今此尤翁与先师之论。其欠却一贯者。设有所未极。其于说分殊之义。犹之无爽。(农岩问目。亦以分殊之说。解天命之性。则未及于一原之义而言也。此为可欠。然其所见分殊之性。则又未尝非宲理宲见。而非为有歉也。尤翁先师之见。亦同此分殊。)则顾不足比之退之三品之语。(退之三品之语。即孔子相近之义。而退之不说气字。孔子亦不曾说气字。今三先生之说性不同。即孟子三性之义。而孟子虽少个气字。却更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则已说一原之意。三先生皆言其不同者是理。则比孟子又分明。而却不说一原。此可见先辈造道立言之宲。又可见三先生所造较杨韩越不同。但欠一贯。)而可毕列为诐邪之黜耶。稊稗五谷优劣判然。而孟子犹曰五谷之不熟。不如稊稗之熟。况一原分殊皆宲理。而只有体分之别。则其分殊之精。顾不犹愈于一原之未精耶。况自栗谷既的说理同而性不同之义。则尤翁之于性一原。未有明教。自不为怪。而江门之不肯说性一原。其实又固无所受也耶。今以性皆作五常。又以五常作人物之一原。而思以易世。至以政禁加之异己之见者。所由来则渐矣。究其实则无或近于疏率乎。盖五常在人为本然。而本然又所以为一原。故转转推测。遂至如此。然孔子曰仁者见之以为仁。知者见之以为知。君子之道鲜矣。仁者见知。亦以为仁。知者见仁。亦以
字。既以为的见而尽好。则其不以欠个气字。拟之诐邪。而当用不用当刻不刻也必矣。今此尤翁与先师之论。其欠却一贯者。设有所未极。其于说分殊之义。犹之无爽。(农岩问目。亦以分殊之说。解天命之性。则未及于一原之义而言也。此为可欠。然其所见分殊之性。则又未尝非宲理宲见。而非为有歉也。尤翁先师之见。亦同此分殊。)则顾不足比之退之三品之语。(退之三品之语。即孔子相近之义。而退之不说气字。孔子亦不曾说气字。今三先生之说性不同。即孟子三性之义。而孟子虽少个气字。却更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则已说一原之意。三先生皆言其不同者是理。则比孟子又分明。而却不说一原。此可见先辈造道立言之宲。又可见三先生所造较杨韩越不同。但欠一贯。)而可毕列为诐邪之黜耶。稊稗五谷优劣判然。而孟子犹曰五谷之不熟。不如稊稗之熟。况一原分殊皆宲理。而只有体分之别。则其分殊之精。顾不犹愈于一原之未精耶。况自栗谷既的说理同而性不同之义。则尤翁之于性一原。未有明教。自不为怪。而江门之不肯说性一原。其实又固无所受也耶。今以性皆作五常。又以五常作人物之一原。而思以易世。至以政禁加之异己之见者。所由来则渐矣。究其实则无或近于疏率乎。盖五常在人为本然。而本然又所以为一原。故转转推测。遂至如此。然孔子曰仁者见之以为仁。知者见之以为知。君子之道鲜矣。仁者见知。亦以为仁。知者见仁。亦以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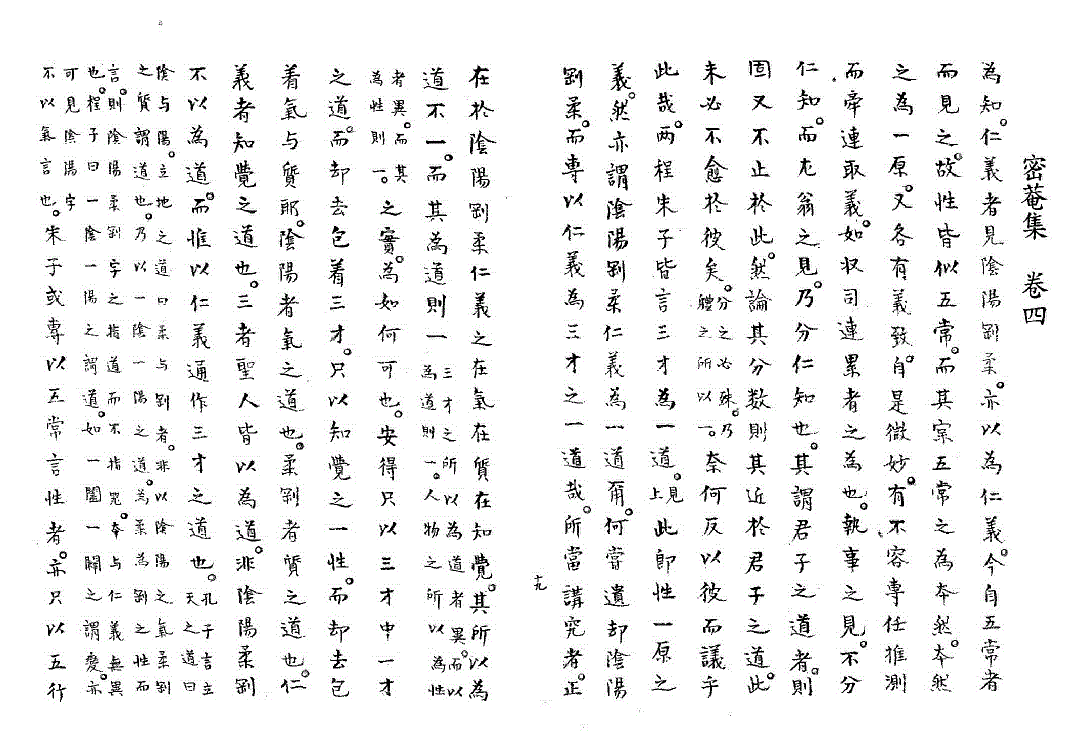 为知。仁义者见阴阳刚柔。亦以为仁义。今自五常者而见之。故性皆似五常。而其宲五常之为本然。本然之为一原。又各有义致。自是微妙。有不容专任推测而牵连取义。如收司连累者之为也。执事之见。不分仁知。而尤翁之见。乃分仁知也。其谓君子之道者。则固又不止于此。然论其分数则其近于君子之道。此未必不愈于彼矣。(分之必殊。乃体之所以一。)奈何反以彼而议乎此哉。两程朱子皆言三才为一道。(见上)此即性一原之义。然亦谓阴阳刚柔仁义为一道尔。何尝遗却阴阳刚柔。而专以仁义为三才之一道哉。所当讲究者。正在于阴阳刚柔仁义之在气在质在知觉。其所以为道不一。而其为道则一。(三才之所以为道者异。而以为道则一。人物之所以为性者异。而其为性则一。)之实。为如何可也。安得只以三才中一才之道。而却去包着三才。只以知觉之一性。而却去包着气与质耶。阴阳者气之道也。柔刚者质之道也。仁义者知觉之道也。三者圣人皆以为道。非阴阳柔刚不以为道。而惟以仁义通作三才之道也。(孔子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者。非以阴阳之气柔刚之质谓道也。乃以一阴一阳之道。为柔为刚之性而言。则阴阳柔刚字之指道而不指器。本与仁义无异也。程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一阖一辟之谓变。亦可见阴阳字不以气言也。)朱子或专以五常言性者。亦只以五行
为知。仁义者见阴阳刚柔。亦以为仁义。今自五常者而见之。故性皆似五常。而其宲五常之为本然。本然之为一原。又各有义致。自是微妙。有不容专任推测而牵连取义。如收司连累者之为也。执事之见。不分仁知。而尤翁之见。乃分仁知也。其谓君子之道者。则固又不止于此。然论其分数则其近于君子之道。此未必不愈于彼矣。(分之必殊。乃体之所以一。)奈何反以彼而议乎此哉。两程朱子皆言三才为一道。(见上)此即性一原之义。然亦谓阴阳刚柔仁义为一道尔。何尝遗却阴阳刚柔。而专以仁义为三才之一道哉。所当讲究者。正在于阴阳刚柔仁义之在气在质在知觉。其所以为道不一。而其为道则一。(三才之所以为道者异。而以为道则一。人物之所以为性者异。而其为性则一。)之实。为如何可也。安得只以三才中一才之道。而却去包着三才。只以知觉之一性。而却去包着气与质耶。阴阳者气之道也。柔刚者质之道也。仁义者知觉之道也。三者圣人皆以为道。非阴阳柔刚不以为道。而惟以仁义通作三才之道也。(孔子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者。非以阴阳之气柔刚之质谓道也。乃以一阴一阳之道。为柔为刚之性而言。则阴阳柔刚字之指道而不指器。本与仁义无异也。程子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如一阖一辟之谓变。亦可见阴阳字不以气言也。)朱子或专以五常言性者。亦只以五行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0L 页
 之为类。本然之无二。而借此名彼而已。若人物五常全偏之分则自在焉。(非但答黄道夫,余方叔书为然。其答胡广仲,陈才卿中庸或问之类。亦皆如此。)全偏之分。既不能无。则所谓五常者。便不成一原之性体矣。五常既不成一原。则无血气知觉者之为五常。便无来历矣。古之圣人所以分三才立道者。实为顺性命之理。入神之精义。而孔子又述古立言。诚实的确。则乃其义不可易矣。故朱子又说三才之别一原正义既明且备。(见上下)非谓三才之为物。其性无别。而可一截以人道之仁义为性也。此固不可害辞害志处。而若其以五常为性之一原。而逐物全具之论。则又未知始于何世何人。而其非孔孟之言则明矣。求之大原之内则无矣。夫所谓性者。成之之理。而成之之理。无不可率者也。性无不可率。而率性为道。故曰可离非道也。如有不可率之性。则是有可离之道也。既曰可离非道。则不可率者非性矣。今也徒喜性同性一之题目。不复深察一物全性万性一性之实。而欲以人道之五常。拟之庶性之一原者。是盖又将以庶物之道。拟之人性之一原。而亦莫知其不可也。(朱子虽有以性作五常处。今观其谓药性仁义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物皆禀得健顺五常之性。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蜂蚁之义。
之为类。本然之无二。而借此名彼而已。若人物五常全偏之分则自在焉。(非但答黄道夫,余方叔书为然。其答胡广仲,陈才卿中庸或问之类。亦皆如此。)全偏之分。既不能无。则所谓五常者。便不成一原之性体矣。五常既不成一原。则无血气知觉者之为五常。便无来历矣。古之圣人所以分三才立道者。实为顺性命之理。入神之精义。而孔子又述古立言。诚实的确。则乃其义不可易矣。故朱子又说三才之别一原正义既明且备。(见上下)非谓三才之为物。其性无别。而可一截以人道之仁义为性也。此固不可害辞害志处。而若其以五常为性之一原。而逐物全具之论。则又未知始于何世何人。而其非孔孟之言则明矣。求之大原之内则无矣。夫所谓性者。成之之理。而成之之理。无不可率者也。性无不可率。而率性为道。故曰可离非道也。如有不可率之性。则是有可离之道也。既曰可离非道。则不可率者非性矣。今也徒喜性同性一之题目。不复深察一物全性万性一性之实。而欲以人道之五常。拟之庶性之一原者。是盖又将以庶物之道。拟之人性之一原。而亦莫知其不可也。(朱子虽有以性作五常处。今观其谓药性仁义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五行各专其一。人物皆禀得健顺五常之性。牛之性顺。马之性健。即健顺之性。虎狼之仁。蜂蚁之义。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1H 页
 即五常之性等语。又观子融认知觉为性之语。则其谓物性仁义者。亦只以其同为本然而言。其谓本然者。又直指其寒热之理与木理金理而言也。非谓木理金理非本然非一原。而别有五常全性。如近来人物均五常之说也。又观朱子仁义礼智与性为体。及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元不曾禀得此道理。不见仁义礼智之彷绋小小底。不顺恁地分仁义。其所以为是物之理。未尝不具等语。则可见仁义礼智固是性。而既曰与为体。则亦有分别。又其意非谓物物之性。皆为仁义。而又非谓不见仁义彷佛之中。别有有而不可率之全五常。如今性全五常而用不达之说也。且朱子虽曰只以四字言之最端的。然其论五常则只言五行各专其一。人兼备此性。而又乃说性同气异。自然同得。通天下一性。则其谓同谓一者之非谓均五常。又可知矣。孔子之一原。但言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一以贯之。而其言仁义。乃分三才而属之于人。子思之一原。但言天命之谓性。而其言达德之仁智。无施及于物性之意。孟子之一原。但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而其言仁义礼智。乃以人心四端为说。而庶物则无与焉。至于大原之义。则又无出于孔孟已言者之外。而一原之五常。则求之至白首。卒不见焉。不知何时天赖之灵。得一见而死也。程子论鬼神而有心病目病之语。今此五常一原。莫殆甚焉。)故弟则常以为五常之为一原。特是衰季之讹言也。凡此大义。苟非原本宲体及圣贤正训。而好立新奇之题目。则虽以其微密难辨。世乏眼目。而见容于一时。甚病于实理。非如禀赋为性。密不具信性之义。虽若卑近。其实自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考三王而不谬者也。此其为虚宲真假。又岂得为同年而语者哉。况所谓一原之性。亦既曰性矣。初不在于禀赋为性。密不具信性之外。而与所以为分珠者。非有两性矣。则其所倚拟。又
即五常之性等语。又观子融认知觉为性之语。则其谓物性仁义者。亦只以其同为本然而言。其谓本然者。又直指其寒热之理与木理金理而言也。非谓木理金理非本然非一原。而别有五常全性。如近来人物均五常之说也。又观朱子仁义礼智与性为体。及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元不曾禀得此道理。不见仁义礼智之彷绋小小底。不顺恁地分仁义。其所以为是物之理。未尝不具等语。则可见仁义礼智固是性。而既曰与为体。则亦有分别。又其意非谓物物之性。皆为仁义。而又非谓不见仁义彷佛之中。别有有而不可率之全五常。如今性全五常而用不达之说也。且朱子虽曰只以四字言之最端的。然其论五常则只言五行各专其一。人兼备此性。而又乃说性同气异。自然同得。通天下一性。则其谓同谓一者之非谓均五常。又可知矣。孔子之一原。但言易有太极。神妙万物。物与无妄。一以贯之。而其言仁义。乃分三才而属之于人。子思之一原。但言天命之谓性。而其言达德之仁智。无施及于物性之意。孟子之一原。但言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而其言仁义礼智。乃以人心四端为说。而庶物则无与焉。至于大原之义。则又无出于孔孟已言者之外。而一原之五常。则求之至白首。卒不见焉。不知何时天赖之灵。得一见而死也。程子论鬼神而有心病目病之语。今此五常一原。莫殆甚焉。)故弟则常以为五常之为一原。特是衰季之讹言也。凡此大义。苟非原本宲体及圣贤正训。而好立新奇之题目。则虽以其微密难辨。世乏眼目。而见容于一时。甚病于实理。非如禀赋为性。密不具信性之义。虽若卑近。其实自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考三王而不谬者也。此其为虚宲真假。又岂得为同年而语者哉。况所谓一原之性。亦既曰性矣。初不在于禀赋为性。密不具信性之外。而与所以为分珠者。非有两性矣。则其所倚拟。又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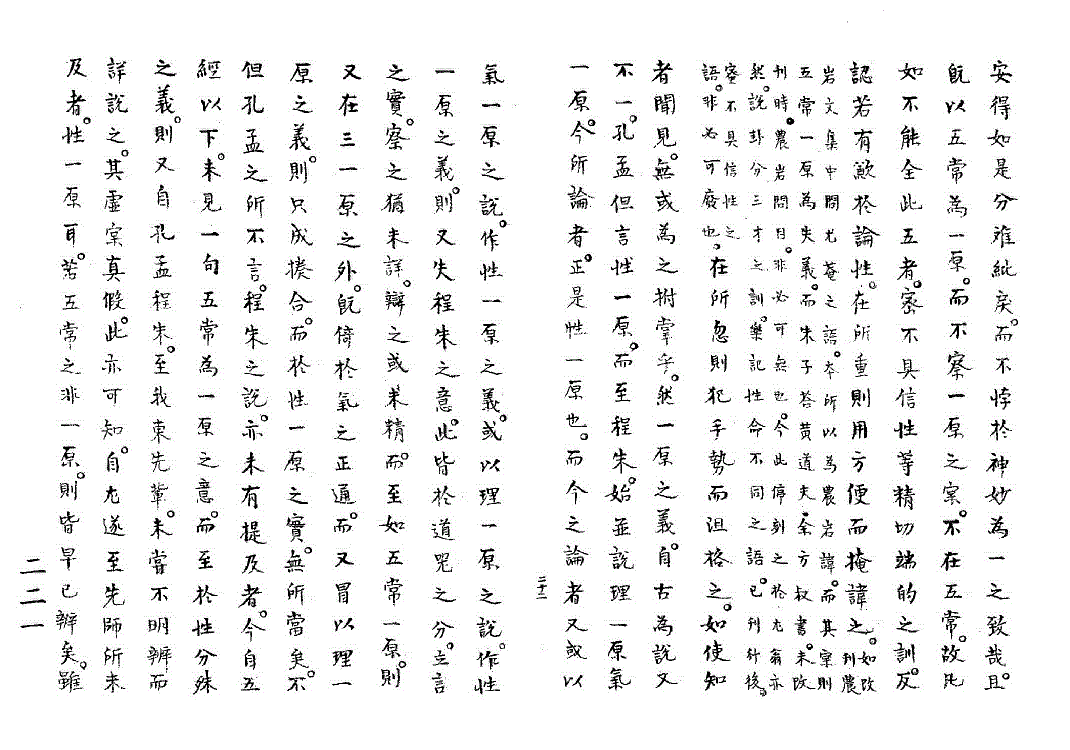 安得如是分离纰戾。而不悖于神妙为一之致哉。且既以五常为一原。而不察一原之宲。不在五常。故凡如不能全此五者。密不具信性等精切端的之训。反认若有歉于论性。在所重则用方便而掩讳之。(如改刊农岩文集中问尤庵之语。本所以为农岩讳。而其宲则五常一原为失义。而朱子答黄道夫,余方叔书。未改刊时。农岩问目。非必可无也。今此停刻之于尤翁亦然。说卦分三才之训。乐记性命不同之语。已刊行后。蜜不具信性之语。非必可废也。)在所忽则犯手势而沮格之。如使知者闻见。无或为之拊掌乎。然一原之义。自古为说又不一。孔孟但言性一原。而至程朱。始并说理一原气一原。今所论者。正是性一原也。而今之论者又或以气一原之说。作性一原之义。或以理一原之说。作性一原之义。则又失程朱之意。此皆于道器之分。立言之实。察之犹未详。辩之或未精。而至如五常一原。则又在三一原之外。既倚于气之正通。而又冒以理一原之义。则只成揍合。而于性一原之实。无所当矣。不但孔孟之所不言。程朱之说。亦未有提及者。今自五经以下。未见一句五常为一原之意。而至于性分殊之义。则又自孔孟程朱。至我东先辈。未尝不明辨而详说之。其虚宲真假。此亦可知。自尤遂至先师所未及者。性一原耳。若五常之非一原。则皆早已辨矣。虽
安得如是分离纰戾。而不悖于神妙为一之致哉。且既以五常为一原。而不察一原之宲。不在五常。故凡如不能全此五者。密不具信性等精切端的之训。反认若有歉于论性。在所重则用方便而掩讳之。(如改刊农岩文集中问尤庵之语。本所以为农岩讳。而其宲则五常一原为失义。而朱子答黄道夫,余方叔书。未改刊时。农岩问目。非必可无也。今此停刻之于尤翁亦然。说卦分三才之训。乐记性命不同之语。已刊行后。蜜不具信性之语。非必可废也。)在所忽则犯手势而沮格之。如使知者闻见。无或为之拊掌乎。然一原之义。自古为说又不一。孔孟但言性一原。而至程朱。始并说理一原气一原。今所论者。正是性一原也。而今之论者又或以气一原之说。作性一原之义。或以理一原之说。作性一原之义。则又失程朱之意。此皆于道器之分。立言之实。察之犹未详。辩之或未精。而至如五常一原。则又在三一原之外。既倚于气之正通。而又冒以理一原之义。则只成揍合。而于性一原之实。无所当矣。不但孔孟之所不言。程朱之说。亦未有提及者。今自五经以下。未见一句五常为一原之意。而至于性分殊之义。则又自孔孟程朱。至我东先辈。未尝不明辨而详说之。其虚宲真假。此亦可知。自尤遂至先师所未及者。性一原耳。若五常之非一原。则皆早已辨矣。虽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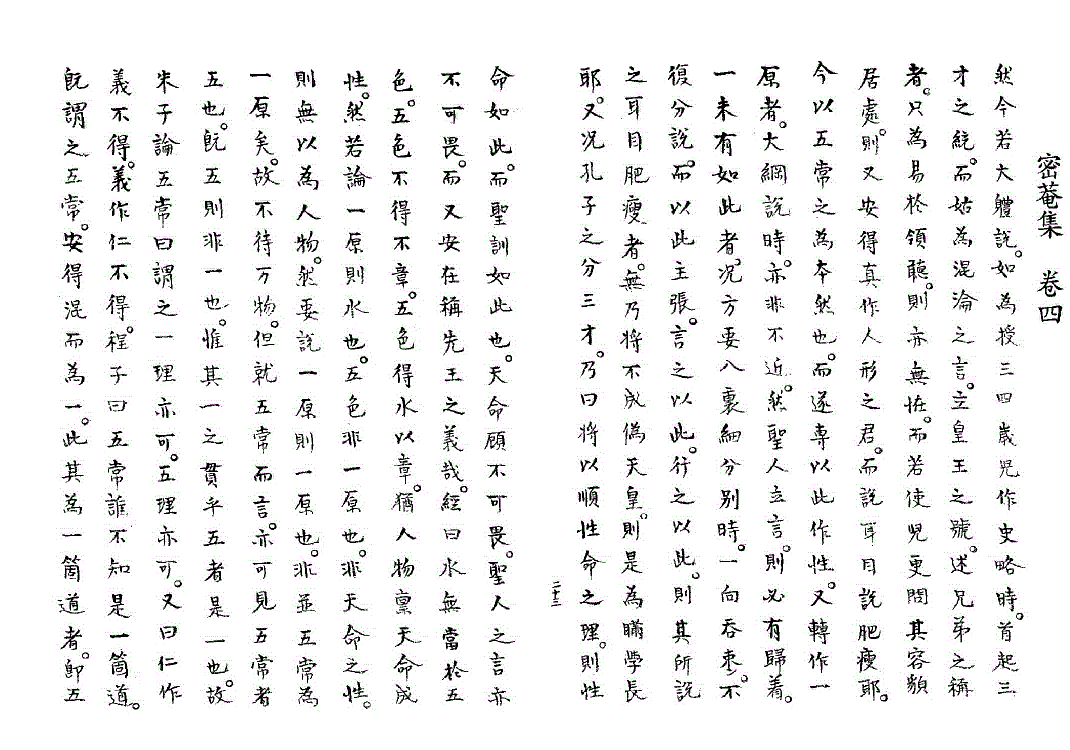 然今若大体说。如为授三四岁儿作史略时。首起三才之统。而姑为混沦之言。立皇王之号。述兄弟之称者。只为易于领听。则亦无怪。而若使儿更问其容貌居处。则又安得真作人形之君。而说耳目说肥瘦耶。今以五常之为本然也。而遂专以此作性。又转作一原者。大纲说时。亦非不近。然圣人立言。则必有归着。一未有如此者。况方要入里细分别时。一向吞枣。不复分说。而以此主张。言之以此。行之以此。则其所说之耳目肥瘦者。无乃将不成伪天皇。则是为瞒学长耶。又况孔子之分三才。乃曰将以顺性命之理。则性命如此。而圣训如此也。天命顾不可畏。圣人之言亦不可畏。而又安在称先王之义哉。经曰水无当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得水以章。犹人物禀天命成性。然若论一原则水也。五色非一原也。非天命之性。则无以为人物。然要说一原则一原也。非并五常为一原矣。故不待万物。但就五常而言。亦可见五常者五也。既五则非一也。惟其一之贯乎五者是一也。故朱子论五常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又曰仁作义不得。义作仁不得。程子曰五常谁不知是一个道。既谓之五常。安得混而为一。此其为一个道者。即五
然今若大体说。如为授三四岁儿作史略时。首起三才之统。而姑为混沦之言。立皇王之号。述兄弟之称者。只为易于领听。则亦无怪。而若使儿更问其容貌居处。则又安得真作人形之君。而说耳目说肥瘦耶。今以五常之为本然也。而遂专以此作性。又转作一原者。大纲说时。亦非不近。然圣人立言。则必有归着。一未有如此者。况方要入里细分别时。一向吞枣。不复分说。而以此主张。言之以此。行之以此。则其所说之耳目肥瘦者。无乃将不成伪天皇。则是为瞒学长耶。又况孔子之分三才。乃曰将以顺性命之理。则性命如此。而圣训如此也。天命顾不可畏。圣人之言亦不可畏。而又安在称先王之义哉。经曰水无当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五色得水以章。犹人物禀天命成性。然若论一原则水也。五色非一原也。非天命之性。则无以为人物。然要说一原则一原也。非并五常为一原矣。故不待万物。但就五常而言。亦可见五常者五也。既五则非一也。惟其一之贯乎五者是一也。故朱子论五常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又曰仁作义不得。义作仁不得。程子曰五常谁不知是一个道。既谓之五常。安得混而为一。此其为一个道者。即五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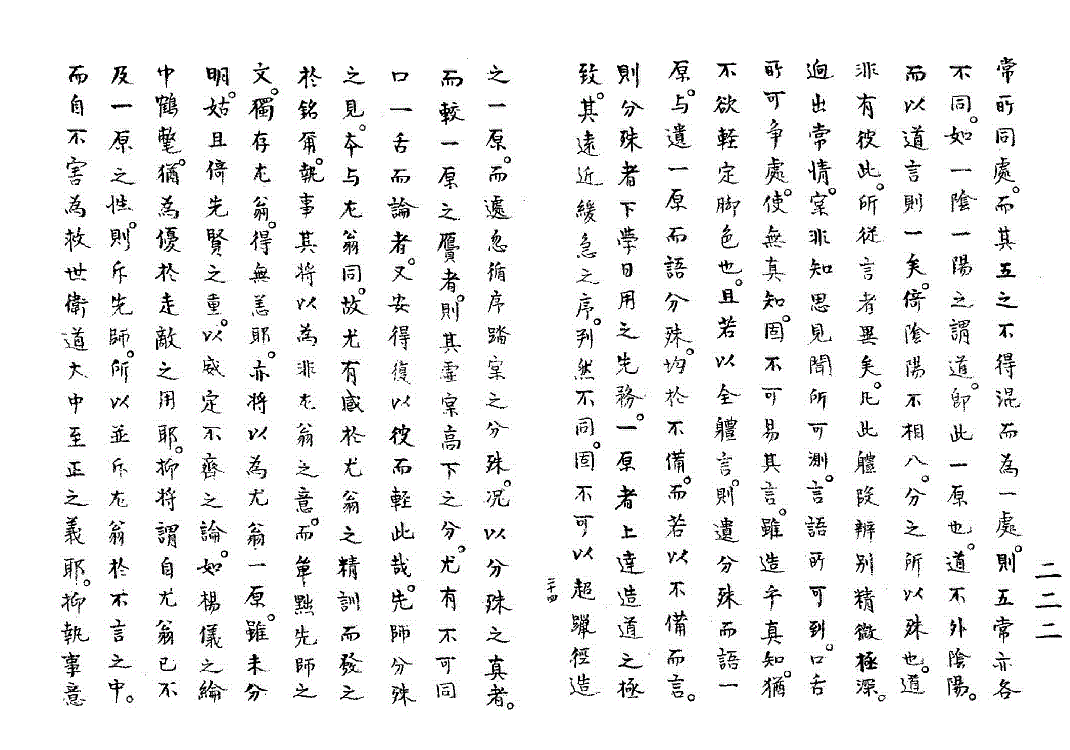 常所同处。而其五之不得混而为一处。则五常亦各不同。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此一原也。道不外阴阳。而以道言则一矣。倚阴阳不相入。分之所以殊也。道非有彼此。所从言者异矣。凡此体段辨别精微极深。迥出常情。宲非知思见闻所可测。言语所可到。口舌所可争处。使无真知。固不可易其言。虽造乎真知。犹不欲轻定脚色也。且若以全体言。则遗分殊而语一原。与遗一原而语分殊。均于不备。而若以不备而言。则分殊者下学日用之先务。一原者上达造道之极致。其远近缓急之序。判然不同。固不可以超躐径造之一原。而遽忽循序踏宲之分殊。况以分殊之真者。而较一原之赝者。则其虚宲高下之分。尤有不可同口一舌而论者。又安得复以彼而轻此哉。先师分殊之见。本与尤翁同。故尤有感于尤翁之精训而发之于铭尔。执事其将以为非尤翁之意。而单黜先师之文。独存尤翁。得无恙耶。亦将以为尤翁一原。虽未分明。姑且倚先贤之重。以威定不齐之论。如杨仪之纶巾鹤氅。犹为优于走敌之用耶。抑将谓自尤翁已不及一原之性。则斥先师。所以并斥尤翁于不言之中。而自不害为救世卫道大中至正之义耶。抑执事意
常所同处。而其五之不得混而为一处。则五常亦各不同。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此一原也。道不外阴阳。而以道言则一矣。倚阴阳不相入。分之所以殊也。道非有彼此。所从言者异矣。凡此体段辨别精微极深。迥出常情。宲非知思见闻所可测。言语所可到。口舌所可争处。使无真知。固不可易其言。虽造乎真知。犹不欲轻定脚色也。且若以全体言。则遗分殊而语一原。与遗一原而语分殊。均于不备。而若以不备而言。则分殊者下学日用之先务。一原者上达造道之极致。其远近缓急之序。判然不同。固不可以超躐径造之一原。而遽忽循序踏宲之分殊。况以分殊之真者。而较一原之赝者。则其虚宲高下之分。尤有不可同口一舌而论者。又安得复以彼而轻此哉。先师分殊之见。本与尤翁同。故尤有感于尤翁之精训而发之于铭尔。执事其将以为非尤翁之意。而单黜先师之文。独存尤翁。得无恙耶。亦将以为尤翁一原。虽未分明。姑且倚先贤之重。以威定不齐之论。如杨仪之纶巾鹤氅。犹为优于走敌之用耶。抑将谓自尤翁已不及一原之性。则斥先师。所以并斥尤翁于不言之中。而自不害为救世卫道大中至正之义耶。抑执事意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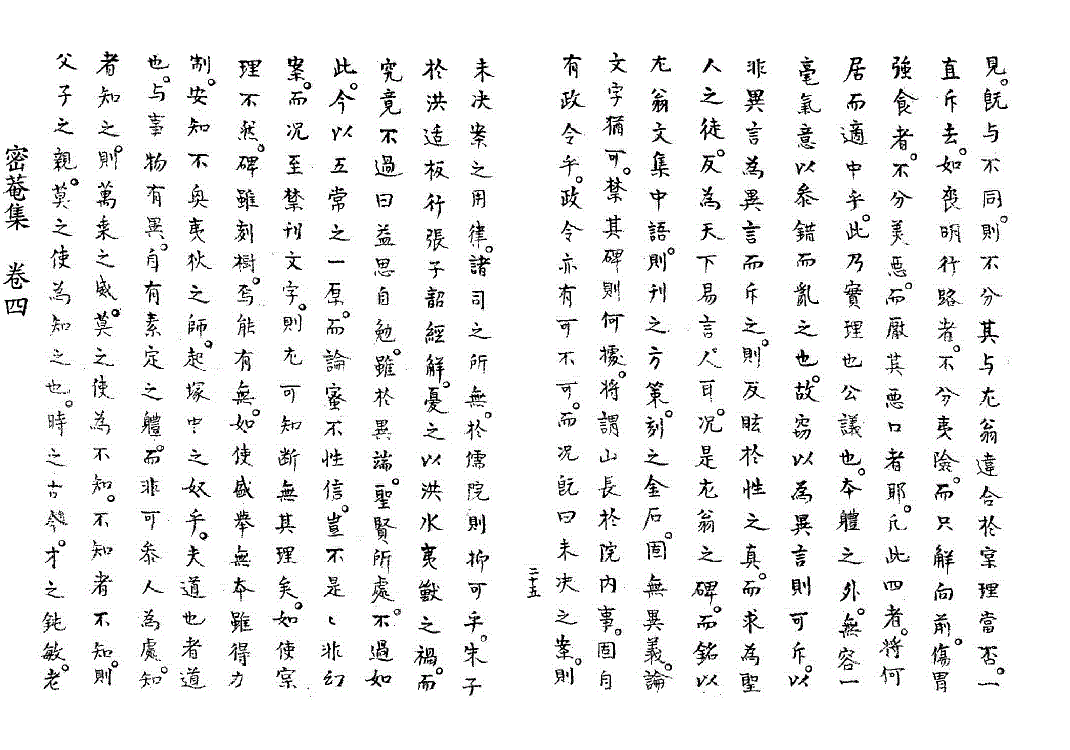 见。既与不同。则不分其与尤翁违合于宲理当否。一直斥去。如丧明行路者。不分夷险。而只解向前。伤胃强食者。不分美恶。而厌其恶口者耶。凡此四者。将何居而适中乎。此乃实理也公议也。本体之外。无容一毫气意以参错而乱之也。故窃以为异言则可斥。以非异言为异言而斥之。则反眩于性之真。而求为圣人之徒。反为天下易言人耳。况是尤翁之碑。而铭以尤翁文集中语。则刊之方策。刻之金石。固无异义。论文字犹可。禁其碑则何据。将谓山长于院内事。固自有政令乎。政令亦有可不可。而况既曰未决之案。则未决案之用律。诸司之所无。于儒院则抑可乎。朱子于洪适板行张子韶经解。忧之以洪水夷兽之祸。而究竟不过曰益思自勉。虽于异端。圣贤所处。不过如此。今以五常之一原。而论蜜不性信。岂不是是非幻案。而况至禁刊文字。则尤可知断无其理矣。如使宲理不然。碑虽刻树。焉能有无。如使盛举无本虽得力制。安知不兴夷狄之师。起冢中之奴乎。夫道也者道也。与事物有异。自有素定之体。而非可参人为处。知者知之。则万乘之威。莫之使为不知。不知者不知。则父子之亲。莫之使为知之也。时之古今。才之钝敏。老
见。既与不同。则不分其与尤翁违合于宲理当否。一直斥去。如丧明行路者。不分夷险。而只解向前。伤胃强食者。不分美恶。而厌其恶口者耶。凡此四者。将何居而适中乎。此乃实理也公议也。本体之外。无容一毫气意以参错而乱之也。故窃以为异言则可斥。以非异言为异言而斥之。则反眩于性之真。而求为圣人之徒。反为天下易言人耳。况是尤翁之碑。而铭以尤翁文集中语。则刊之方策。刻之金石。固无异义。论文字犹可。禁其碑则何据。将谓山长于院内事。固自有政令乎。政令亦有可不可。而况既曰未决之案。则未决案之用律。诸司之所无。于儒院则抑可乎。朱子于洪适板行张子韶经解。忧之以洪水夷兽之祸。而究竟不过曰益思自勉。虽于异端。圣贤所处。不过如此。今以五常之一原。而论蜜不性信。岂不是是非幻案。而况至禁刊文字。则尤可知断无其理矣。如使宲理不然。碑虽刻树。焉能有无。如使盛举无本虽得力制。安知不兴夷狄之师。起冢中之奴乎。夫道也者道也。与事物有异。自有素定之体。而非可参人为处。知者知之。则万乘之威。莫之使为不知。不知者不知。则父子之亲。莫之使为知之也。时之古今。才之钝敏。老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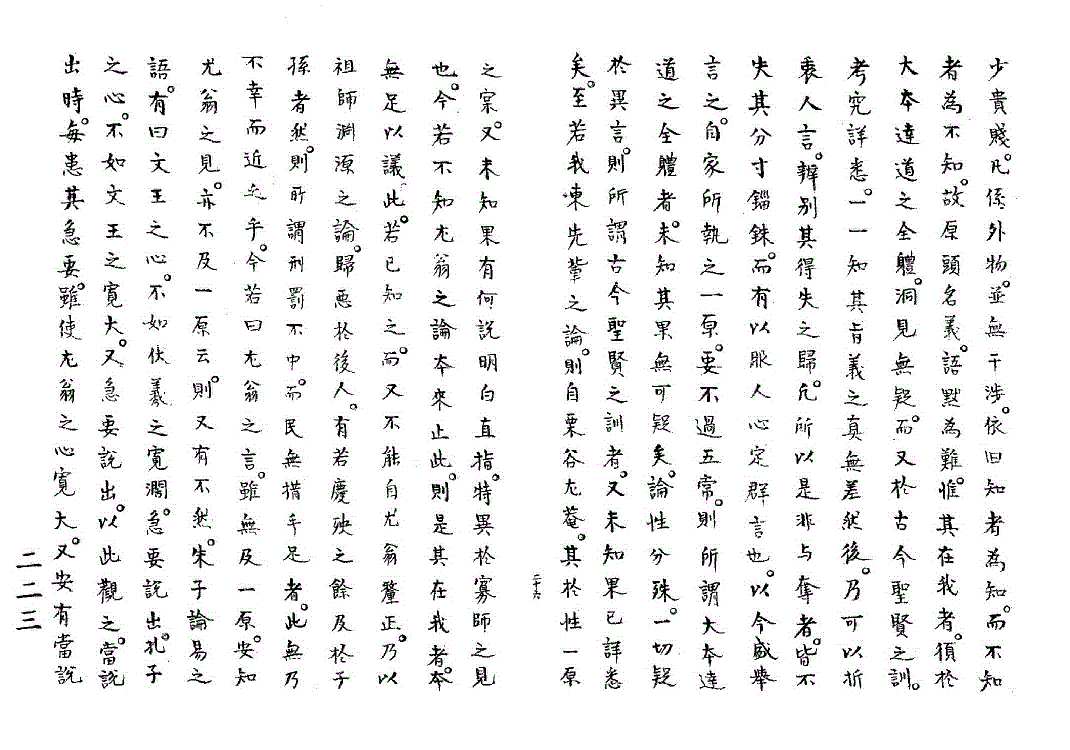 少贵贱。凡系外物。并无干涉。依旧知者为知。而不知者为不知。故原头名义。语默为难。惟其在我者。须于大本达道之全体。洞见无疑。而又于古今圣贤之训。考究详悉。一一知其旨义之真无差然后。乃可以折衷人言。辨别其得失之归。凡所以是非与夺者。皆不失其分寸锱铢。而有以服人心定群言也。以今盛举言之。自家所执之一原。要不过五常。则所谓大本达道之全体者。未知其果无可疑矣。论性分殊。一切疑于异言。则所谓古今圣贤之训者。又未知果已详悉矣。至若我东先辈之论。则自栗谷尤庵。其于性一原之宲。又未知果有何说明白直指。特异于寡师之见也。今若不知尤翁之论本来止此。则是其在我者。本无足以议此。若已知之。而又不能自尤翁釐正。乃以祖师渊源之论。归恶于后人。有若庆殃之馀及于子孙者然。则所谓刑罚不中。而民无措手足者。此无乃不幸而近之乎。今若曰尤翁之言。虽无及一原。安知尤翁之见。亦不及一原云。则又有不然。朱子论易之语。有曰文王之心。不如伏羲之宽阔。急要说出。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宽大。又急要说出。以此观之。当说出时。每患其急要。虽使尤翁之心宽大。又安有当说
少贵贱。凡系外物。并无干涉。依旧知者为知。而不知者为不知。故原头名义。语默为难。惟其在我者。须于大本达道之全体。洞见无疑。而又于古今圣贤之训。考究详悉。一一知其旨义之真无差然后。乃可以折衷人言。辨别其得失之归。凡所以是非与夺者。皆不失其分寸锱铢。而有以服人心定群言也。以今盛举言之。自家所执之一原。要不过五常。则所谓大本达道之全体者。未知其果无可疑矣。论性分殊。一切疑于异言。则所谓古今圣贤之训者。又未知果已详悉矣。至若我东先辈之论。则自栗谷尤庵。其于性一原之宲。又未知果有何说明白直指。特异于寡师之见也。今若不知尤翁之论本来止此。则是其在我者。本无足以议此。若已知之。而又不能自尤翁釐正。乃以祖师渊源之论。归恶于后人。有若庆殃之馀及于子孙者然。则所谓刑罚不中。而民无措手足者。此无乃不幸而近之乎。今若曰尤翁之言。虽无及一原。安知尤翁之见。亦不及一原云。则又有不然。朱子论易之语。有曰文王之心。不如伏羲之宽阔。急要说出。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宽大。又急要说出。以此观之。当说出时。每患其急要。虽使尤翁之心宽大。又安有当说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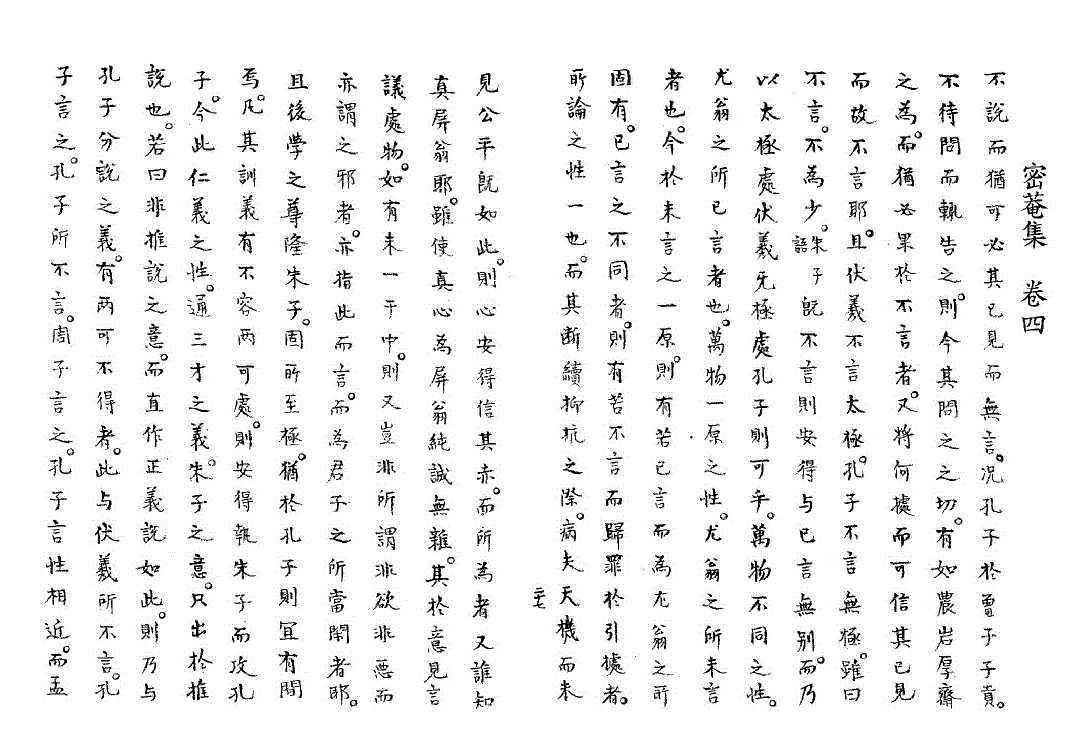 不说而犹可必其已见而无言。况孔子于曾子子贡。不待问而辄告之。则今其问之之切。有如农岩厚斋之为。而犹必果于不言者。又将何据而可信其已见而故不言耶。且伏羲不言太极。孔子不言无极。虽曰不言。不为少。(朱子语)既不言则安得与已言无别。而乃以太极处伏羲无极处孔子则可乎。万物不同之性。尤翁之所已言者也。万物一原之性。尤翁之所未言者也。今于未言之一原。则有若已言而为尤翁之所固有。已言之不同者。则有若不言而归罪于引据者。所论之性一也。而其断续抑抗之际。病夫天机而未见公平既如此。则心安得信其赤。而所为者又谁知真屏翁耶。虽使真心为屏翁纯诚无杂。其于意见言议处物。如有未一于中。则又岂非所谓非欲非恶而亦谓之邪者。亦指此而言。而为君子之所当闲者耶。且后学之尊隆朱子。固所至极。犹于孔子则宜有间焉。凡其训义有不容两可处。则安得执朱子而攻孔子。今此仁义之性。通三才之义。朱子之意。只出于推说也。若曰非推说之意。而直作正义说如此。则乃与孔子分说之义。有两可不得者。此与伏羲所不言。孔子言之。孔子所不言。周子言之。孔子言性相近。而孟
不说而犹可必其已见而无言。况孔子于曾子子贡。不待问而辄告之。则今其问之之切。有如农岩厚斋之为。而犹必果于不言者。又将何据而可信其已见而故不言耶。且伏羲不言太极。孔子不言无极。虽曰不言。不为少。(朱子语)既不言则安得与已言无别。而乃以太极处伏羲无极处孔子则可乎。万物不同之性。尤翁之所已言者也。万物一原之性。尤翁之所未言者也。今于未言之一原。则有若已言而为尤翁之所固有。已言之不同者。则有若不言而归罪于引据者。所论之性一也。而其断续抑抗之际。病夫天机而未见公平既如此。则心安得信其赤。而所为者又谁知真屏翁耶。虽使真心为屏翁纯诚无杂。其于意见言议处物。如有未一于中。则又岂非所谓非欲非恶而亦谓之邪者。亦指此而言。而为君子之所当闲者耶。且后学之尊隆朱子。固所至极。犹于孔子则宜有间焉。凡其训义有不容两可处。则安得执朱子而攻孔子。今此仁义之性。通三才之义。朱子之意。只出于推说也。若曰非推说之意。而直作正义说如此。则乃与孔子分说之义。有两可不得者。此与伏羲所不言。孔子言之。孔子所不言。周子言之。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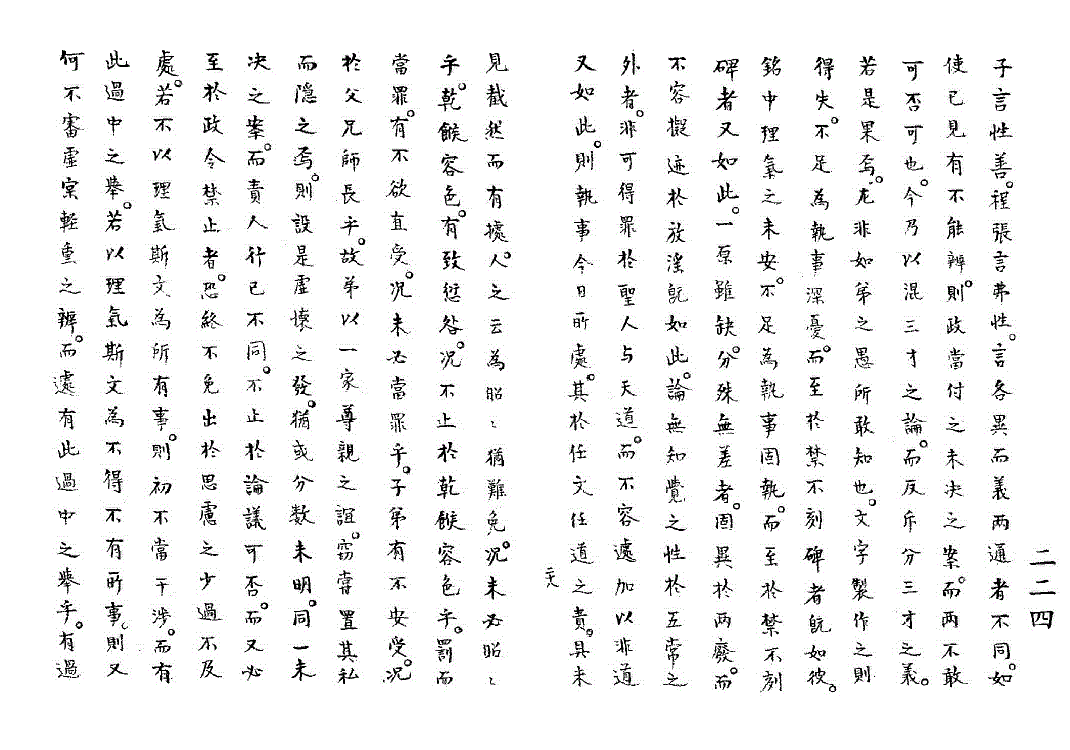 子言性善。程张言弗性。言各异而义两通者不同。如使已见有不能辨。则政当付之未决之案。而两不敢可否可也。今乃以混三才之论。而反斥分三才之义。若是果焉。尤非如弟之愚所敢知也。文字制作之则得失。不足为执事深忧。而至于禁不刻碑者既如彼。铭中理气之未安。不足为执事固执。而至于禁不刻碑者又如此。一原虽缺。分殊无差者。固异于两废。而不容拟迹于放淫既如此。论无知觉之性于五常之外者。非可得罪于圣人与天道。而不容遽加以非道又如此。则执事今日所处。其于任文任道之责。具未见截然而有据。人之云为昭昭犹难免。况未必昭昭乎。乾糇容色。有致愆咎。况不止于乾糇容色乎。罚而当罪。有不欲直受。况未必当罪乎。子弟有不安受。况于父兄师长乎。故弟以一家尊亲之谊。窃尝置其私而隐之焉。则设是虚怀之发。犹或分数未明。同一未决之案。而责人行己不同。不止于论议可否。而又必至于政令禁止者。恐终不免出于思虑之少过不及处。若不以理气斯文为所有事。则初不当干涉。而有此过中之举。若以理气斯文为不得不有所事。则又何不审虚宲轻重之辨。而遽有此过中之举乎。有过
子言性善。程张言弗性。言各异而义两通者不同。如使已见有不能辨。则政当付之未决之案。而两不敢可否可也。今乃以混三才之论。而反斥分三才之义。若是果焉。尤非如弟之愚所敢知也。文字制作之则得失。不足为执事深忧。而至于禁不刻碑者既如彼。铭中理气之未安。不足为执事固执。而至于禁不刻碑者又如此。一原虽缺。分殊无差者。固异于两废。而不容拟迹于放淫既如此。论无知觉之性于五常之外者。非可得罪于圣人与天道。而不容遽加以非道又如此。则执事今日所处。其于任文任道之责。具未见截然而有据。人之云为昭昭犹难免。况未必昭昭乎。乾糇容色。有致愆咎。况不止于乾糇容色乎。罚而当罪。有不欲直受。况未必当罪乎。子弟有不安受。况于父兄师长乎。故弟以一家尊亲之谊。窃尝置其私而隐之焉。则设是虚怀之发。犹或分数未明。同一未决之案。而责人行己不同。不止于论议可否。而又必至于政令禁止者。恐终不免出于思虑之少过不及处。若不以理气斯文为所有事。则初不当干涉。而有此过中之举。若以理气斯文为不得不有所事。则又何不审虚宲轻重之辨。而遽有此过中之举乎。有过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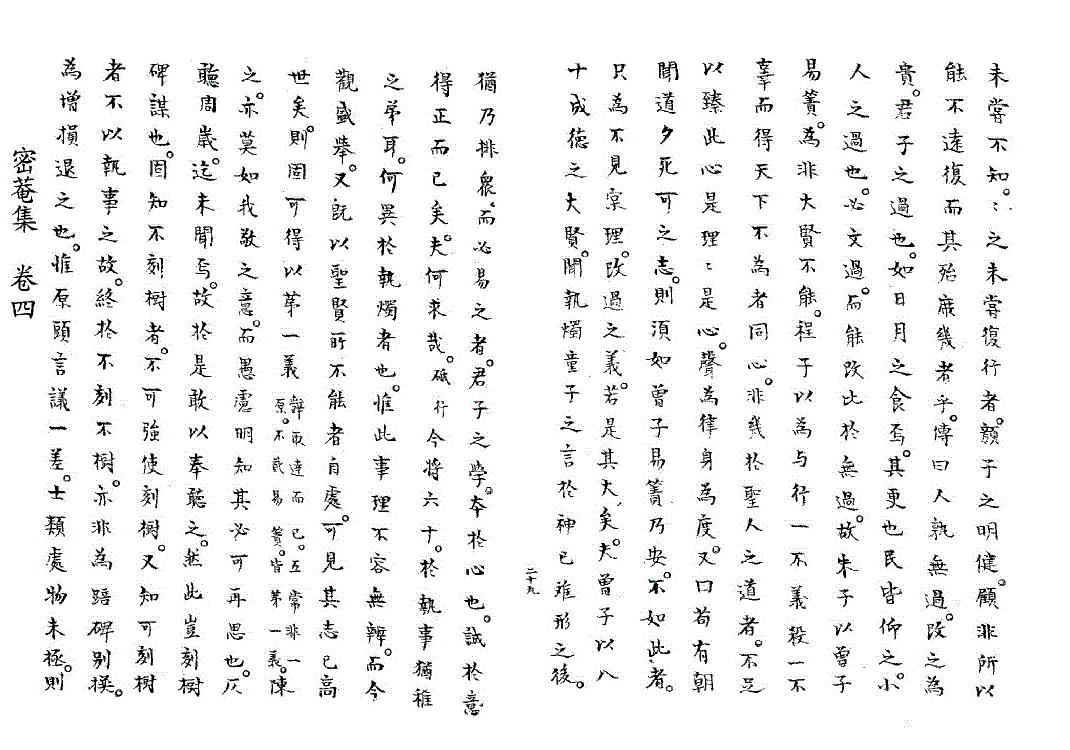 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颜子之明健。顾非所以能不远复而其殆庶几者乎。传曰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民皆仰之。小人之过也。必文过。而能改比于无过。故朱子以曾子易箦。为非大贤不能。程子以为与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同心。非几于圣人之道者。不足以臻此心是理理是心。声为律身为度。又曰苟有朝闻道夕死可之志。则须如曾子易箦乃安。不如此者。只为不见宲理。改过之义。若是其大矣。夫曾子以八十成德之大贤。闻执烛童子之言于神已离形之后。犹乃排众意而必易之者。君子之学。本于心也。诚于得正而已矣。夫何求哉。砥行今将六十。于执事犹稚之弟耳。何异于执烛者也。惟此事理不容无辨。而今观盛举。又既以圣贤所不能者自处。可见其志已高世矣。则固可得以第一义(辞取达而已。五常非一原。不贰易箦。皆第一义。)陈之。亦莫如我敬之意。而愚虑明知其必可再思也。仄听周岁。迄未闻焉。故于是敢以奉听之。然此岂刻树碑谋也。固知不刻树者。不可强使刻树。又知可刻树者不以执事之故。终于不刻不树。亦非为踣碑别撰。为增损退之也。惟原头言议一差。士类处物未极。则
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者。颜子之明健。顾非所以能不远复而其殆庶几者乎。传曰人孰无过。改之为贵。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民皆仰之。小人之过也。必文过。而能改比于无过。故朱子以曾子易箦。为非大贤不能。程子以为与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者同心。非几于圣人之道者。不足以臻此心是理理是心。声为律身为度。又曰苟有朝闻道夕死可之志。则须如曾子易箦乃安。不如此者。只为不见宲理。改过之义。若是其大矣。夫曾子以八十成德之大贤。闻执烛童子之言于神已离形之后。犹乃排众意而必易之者。君子之学。本于心也。诚于得正而已矣。夫何求哉。砥行今将六十。于执事犹稚之弟耳。何异于执烛者也。惟此事理不容无辨。而今观盛举。又既以圣贤所不能者自处。可见其志已高世矣。则固可得以第一义(辞取达而已。五常非一原。不贰易箦。皆第一义。)陈之。亦莫如我敬之意。而愚虑明知其必可再思也。仄听周岁。迄未闻焉。故于是敢以奉听之。然此岂刻树碑谋也。固知不刻树者。不可强使刻树。又知可刻树者不以执事之故。终于不刻不树。亦非为踣碑别撰。为增损退之也。惟原头言议一差。士类处物未极。则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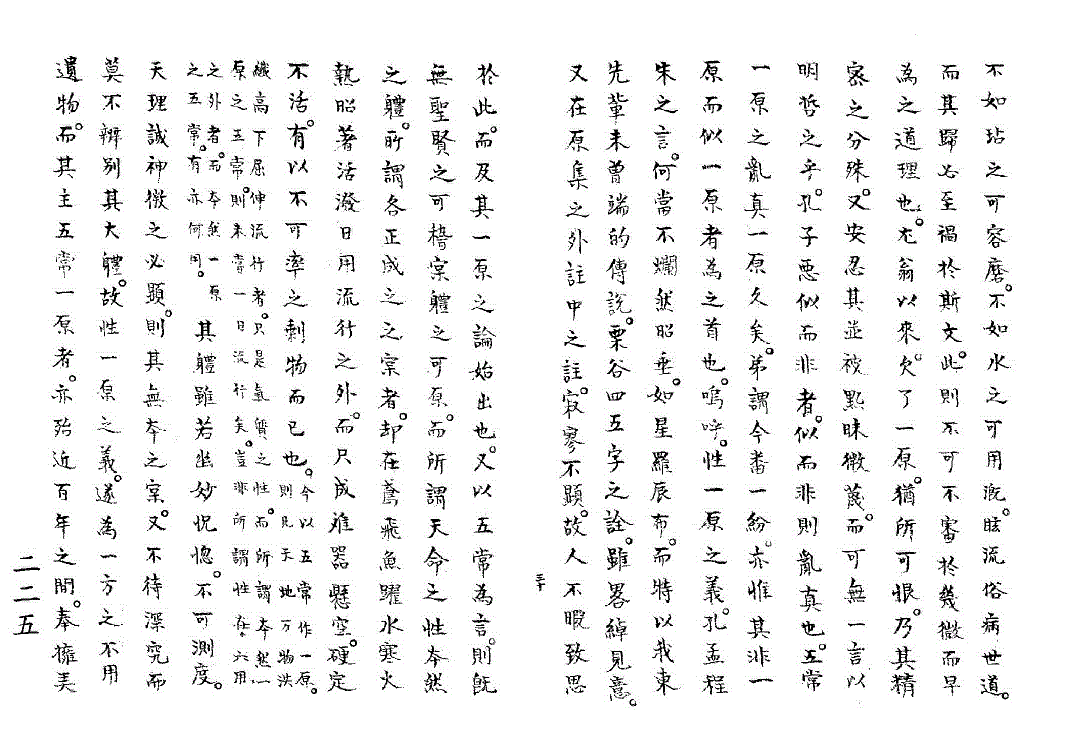 不如玷之可容磨。不如水之可用溉。眩流俗病世道。而其归必至祸于斯文。此则不可不审于几微而早为之道理也。尤翁以来。欠了一原。犹所可恨。乃其精密之分殊。又安忍其并被䵝昧微蔑。而可无一言以明哲之乎。孔子恶似而非者。似而非则乱真也。五常一原之乱真一原久矣。弟谓今番一纷。亦惟其非一原而似一原者为之首也。呜呼。性一原之义。孔孟程朱之言。何当不烂然昭垂。如星罗辰布。而特以我东先辈未曾端的传说。栗谷四五字之诠。虽略绰见意。又在原集之外注中之注。寂寥不显。故人不暇致思于此。而及其一原之论始出也。又以五常为言。则既无圣贤之可稽宲体之可原。而所谓天命之性本然之体。所谓各正成之之宲者。却在鸢飞鱼跃水寒火热昭著活泼日用流行之外。而只成离器悬空。硬定不活。有以不可率之剩物而已也。(今以五常作一原。则凡天地万物洪纤高下屈伸流行者。只是气质之性。而所谓本然一原之五常。则未尝一日流行矣。岂非所谓性在六用之外者。而本然一原之五常。有亦何用。)其体虽若幽妙恍惚。不可测度。天理诚神微之必显。则其无本之宲。又不待深究而莫不辨别其大体。故性一原之义。遂为一方之不用遗物。而其主五常一原者。亦殆近百年之间。奉拥弄
不如玷之可容磨。不如水之可用溉。眩流俗病世道。而其归必至祸于斯文。此则不可不审于几微而早为之道理也。尤翁以来。欠了一原。犹所可恨。乃其精密之分殊。又安忍其并被䵝昧微蔑。而可无一言以明哲之乎。孔子恶似而非者。似而非则乱真也。五常一原之乱真一原久矣。弟谓今番一纷。亦惟其非一原而似一原者为之首也。呜呼。性一原之义。孔孟程朱之言。何当不烂然昭垂。如星罗辰布。而特以我东先辈未曾端的传说。栗谷四五字之诠。虽略绰见意。又在原集之外注中之注。寂寥不显。故人不暇致思于此。而及其一原之论始出也。又以五常为言。则既无圣贤之可稽宲体之可原。而所谓天命之性本然之体。所谓各正成之之宲者。却在鸢飞鱼跃水寒火热昭著活泼日用流行之外。而只成离器悬空。硬定不活。有以不可率之剩物而已也。(今以五常作一原。则凡天地万物洪纤高下屈伸流行者。只是气质之性。而所谓本然一原之五常。则未尝一日流行矣。岂非所谓性在六用之外者。而本然一原之五常。有亦何用。)其体虽若幽妙恍惚。不可测度。天理诚神微之必显。则其无本之宲。又不待深究而莫不辨别其大体。故性一原之义。遂为一方之不用遗物。而其主五常一原者。亦殆近百年之间。奉拥弄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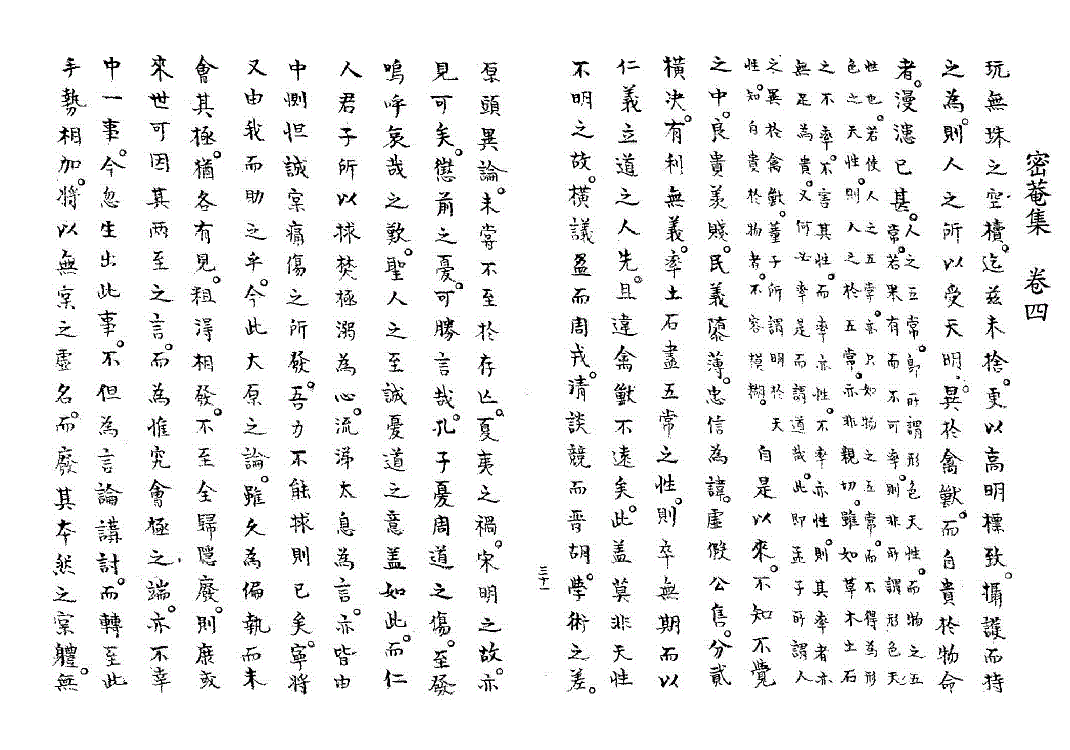 玩无珠之空椟。迄玆未舍。更以高明标致。摄护而持之为。则人之所以受天明。异于禽兽。而自贵于物命者。漫漶已甚。(人之五常。即所谓形色天性。而物之五常。若果有而不可率。则非所谓形色天性也。若使人之五常。亦只如物之五常。而不得为形色之天性。则人之于五常。亦非亲切。虽如草木土石之不率。不害其性。而率亦性。不率亦性。则其率者亦无足为贵。又何必率是而谓道哉。此即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蕫子所谓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者。不容模糊。)自是以来。不知不觉之中。良贵羡贱。民义隳薄。忠信为讳。虚假公售。分贰横决。有利无义。率土石尽五常之性。则卒无期而以仁义立道之人先。且违禽兽不远矣。此盖莫非天性不明之故。横议盈而周戎。清谈竞而晋胡。学术之差。原头异论。未尝不至于存亡。夏夷之祸。宋明之故。亦见可矣。惩前之忧。可胜言哉。孔子忧周道之伤。至发呜呼哀哉之叹。圣人之至诚忧道之意盖如此。而仁人君子所以救焚极溺为心。流涕太息为言。亦皆由中恻怛诚宲痛伤之所发。吾力不能救则已矣。宁将又由我而助之乎。今此大原之论。虽久为偏执而未会其极。犹各有见。粗得相发。不至全归隐废。则庶或来世可因其两至之言。而为惟究会极之端。亦不幸中一事。今忽生出此事。不但为言论讲讨。而转至此手势相加。将以无宲之虚名。而废其本然之宲体。无
玩无珠之空椟。迄玆未舍。更以高明标致。摄护而持之为。则人之所以受天明。异于禽兽。而自贵于物命者。漫漶已甚。(人之五常。即所谓形色天性。而物之五常。若果有而不可率。则非所谓形色天性也。若使人之五常。亦只如物之五常。而不得为形色之天性。则人之于五常。亦非亲切。虽如草木土石之不率。不害其性。而率亦性。不率亦性。则其率者亦无足为贵。又何必率是而谓道哉。此即孟子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蕫子所谓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者。不容模糊。)自是以来。不知不觉之中。良贵羡贱。民义隳薄。忠信为讳。虚假公售。分贰横决。有利无义。率土石尽五常之性。则卒无期而以仁义立道之人先。且违禽兽不远矣。此盖莫非天性不明之故。横议盈而周戎。清谈竞而晋胡。学术之差。原头异论。未尝不至于存亡。夏夷之祸。宋明之故。亦见可矣。惩前之忧。可胜言哉。孔子忧周道之伤。至发呜呼哀哉之叹。圣人之至诚忧道之意盖如此。而仁人君子所以救焚极溺为心。流涕太息为言。亦皆由中恻怛诚宲痛伤之所发。吾力不能救则已矣。宁将又由我而助之乎。今此大原之论。虽久为偏执而未会其极。犹各有见。粗得相发。不至全归隐废。则庶或来世可因其两至之言。而为惟究会极之端。亦不幸中一事。今忽生出此事。不但为言论讲讨。而转至此手势相加。将以无宲之虚名。而废其本然之宲体。无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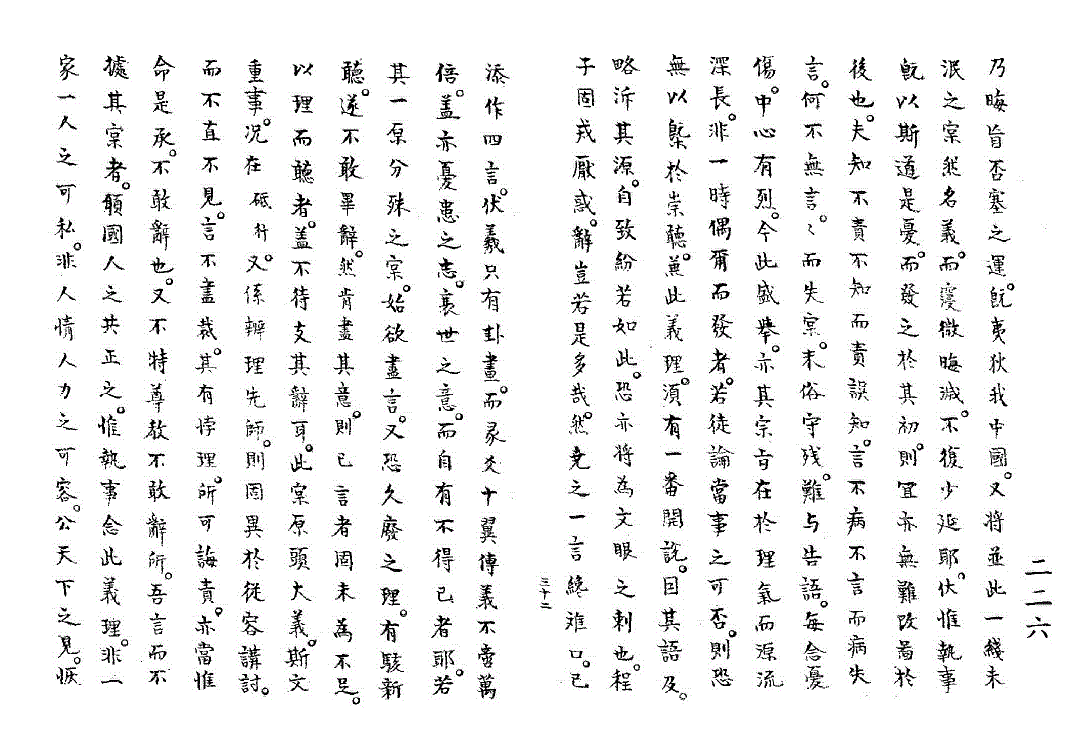 乃晦盲否塞之运。既夷狄我中国。又将并此一线未泯之宲然名义。而䆮微晦灭。不复少延耶。伏惟执事既以斯道是忧。而发之于其初。则宜亦无难改啚于后也。夫知不责不知而责误知。言不病不言而病失言。何不无言。言而失宲。末俗守残。难与告语。每念忧伤。中心有烈。今此盛举。亦其宗旨在于理气而源流深长。非一时偶尔而发者。若徒论当事之可否。则恐无以槩于崇听。兼此义理。须有一番开说。因其语及。略溯其源。自致纷若如此。恐亦将为文眼之刺也。程子固戒厌惑。辞岂若是多哉。然尧之一言才离口。已添作四言。伏羲只有卦画。而彖爻十翼传义不啻万倍。盖亦忧患之志。衰世之意。而自有不得已者耶。若其一原分殊之宲。始欲尽言。又恐久废之理。有骇新听。遂不敢毕辞。然肯尽其意。则已言者固未为不足。以理而听者。盖不待支其辞耳。此宲原头大义。斯文重事。况在砥行。又系辨理先师。则固异于从容讲讨。而不直不见。言不尽裁。其有悖理。所可诲责。亦当惟命是承。不敢辞也。又不特尊教不敢辞所。吾言而不据其宲者。愿国人之共正之。惟执事念此义理。非一家一人之可私。非人情人力之可容。公天下之见。恢
乃晦盲否塞之运。既夷狄我中国。又将并此一线未泯之宲然名义。而䆮微晦灭。不复少延耶。伏惟执事既以斯道是忧。而发之于其初。则宜亦无难改啚于后也。夫知不责不知而责误知。言不病不言而病失言。何不无言。言而失宲。末俗守残。难与告语。每念忧伤。中心有烈。今此盛举。亦其宗旨在于理气而源流深长。非一时偶尔而发者。若徒论当事之可否。则恐无以槩于崇听。兼此义理。须有一番开说。因其语及。略溯其源。自致纷若如此。恐亦将为文眼之刺也。程子固戒厌惑。辞岂若是多哉。然尧之一言才离口。已添作四言。伏羲只有卦画。而彖爻十翼传义不啻万倍。盖亦忧患之志。衰世之意。而自有不得已者耶。若其一原分殊之宲。始欲尽言。又恐久废之理。有骇新听。遂不敢毕辞。然肯尽其意。则已言者固未为不足。以理而听者。盖不待支其辞耳。此宲原头大义。斯文重事。况在砥行。又系辨理先师。则固异于从容讲讨。而不直不见。言不尽裁。其有悖理。所可诲责。亦当惟命是承。不敢辞也。又不特尊教不敢辞所。吾言而不据其宲者。愿国人之共正之。惟执事念此义理。非一家一人之可私。非人情人力之可容。公天下之见。恢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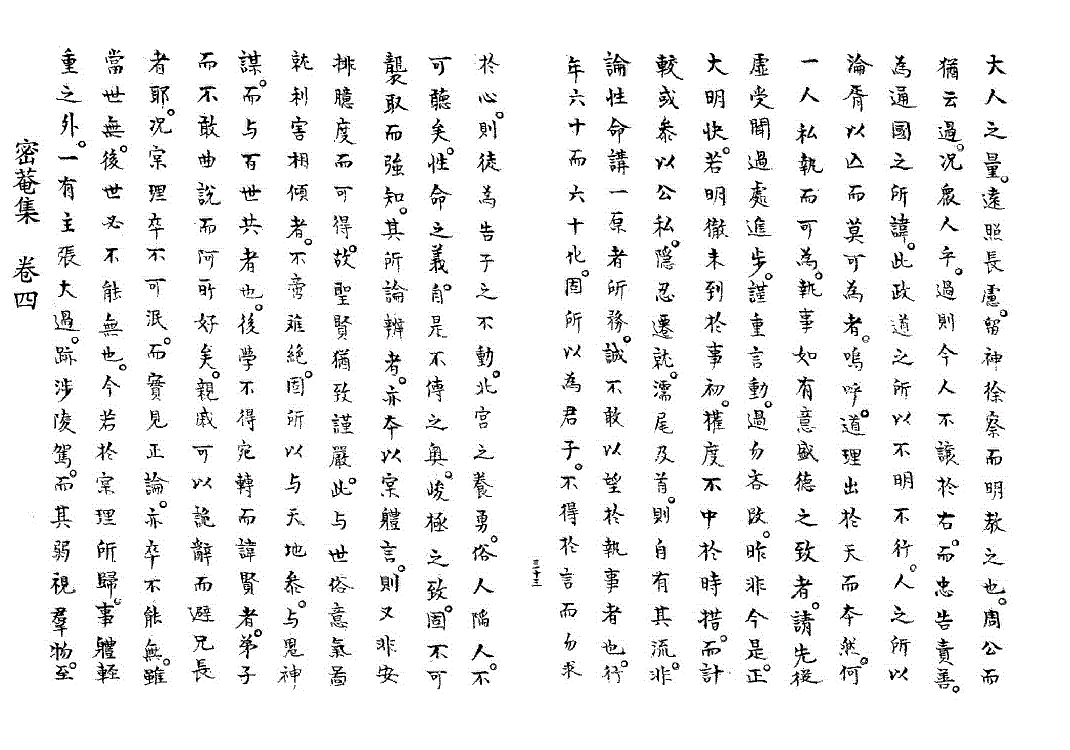 大人之量。远照长虑。留神徐察而明教之也。周公而犹云过。况众人乎。过则今人不让于右。而忠告责善。为通国之所讳。此政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人之所以沦胥以亡而莫可为者。呜呼。道理出于天而本然。何一人私执而可为。执事如有意盛德之致者。请先从虚受闻过处进步。谨重言动。过勿吝改。昨非今是。正大明快。若明彻未到于事初。权度不中于时措。而计较或参以公私。隐忍迁就。濡尾及首。则自有其流。非论性命讲一原者所务。诚不敢以望于执事者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固所以为君子。不得于言而勿求于心。则徒为告子之不动。兆宫之养勇。俗人陷人。不可听矣。性命之义。自是不传之奥。峻极之致。固不可袭取而强知。其所论辨者。亦本以宲体言。则又非安排臆度而可得。故圣贤犹致谨严。此与世俗意气啚就利害相倾者。不啻离绝。固所以与天地参。与鬼神谋。而与百世共者也。后学不得宛转而讳贤者。弟子而不敢曲说而阿所好矣。亲戚可以诡辞而避兄长者耶。况宲理卒不可泯。而实见正论。亦卒不能无。虽当世无。后世必不能无也。今若于宲理所归。事体轻重之外。一有主张大过。迹涉陵驾。而其弱视群物。至
大人之量。远照长虑。留神徐察而明教之也。周公而犹云过。况众人乎。过则今人不让于右。而忠告责善。为通国之所讳。此政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人之所以沦胥以亡而莫可为者。呜呼。道理出于天而本然。何一人私执而可为。执事如有意盛德之致者。请先从虚受闻过处进步。谨重言动。过勿吝改。昨非今是。正大明快。若明彻未到于事初。权度不中于时措。而计较或参以公私。隐忍迁就。濡尾及首。则自有其流。非论性命讲一原者所务。诚不敢以望于执事者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固所以为君子。不得于言而勿求于心。则徒为告子之不动。兆宫之养勇。俗人陷人。不可听矣。性命之义。自是不传之奥。峻极之致。固不可袭取而强知。其所论辨者。亦本以宲体言。则又非安排臆度而可得。故圣贤犹致谨严。此与世俗意气啚就利害相倾者。不啻离绝。固所以与天地参。与鬼神谋。而与百世共者也。后学不得宛转而讳贤者。弟子而不敢曲说而阿所好矣。亲戚可以诡辞而避兄长者耶。况宲理卒不可泯。而实见正论。亦卒不能无。虽当世无。后世必不能无也。今若于宲理所归。事体轻重之外。一有主张大过。迹涉陵驾。而其弱视群物。至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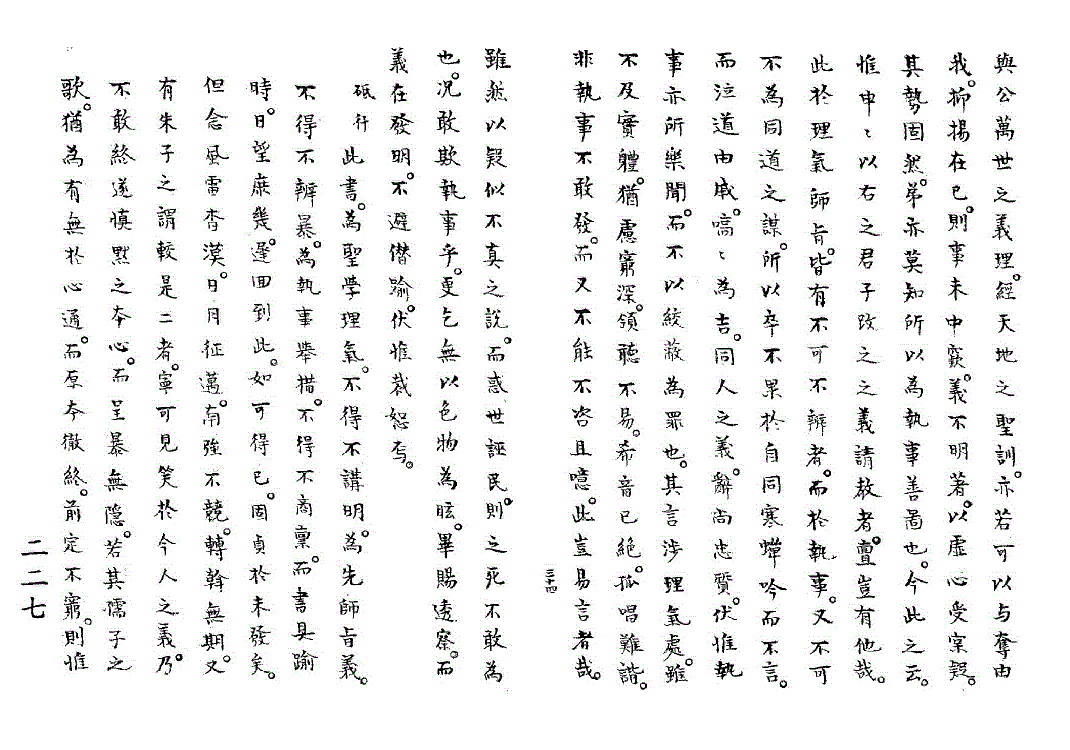 与公万世之义理。经天地之圣训。亦若可以与夺由我。抑扬在己。则事未中窾。义不明著。以虚心受宲疑。其势固然。弟亦莫知所以为执事善啚也。今此之云。惟申申以右之君子改之之义请教者。亶岂有他哉。此于理气师旨。皆有不可不辨者。而于执事。又不可不为同道之谋。所以卒不果于自同寒蝉吟而不言。而泣道由戚。嗃嗃为吉。同人之义。辞尚忠质。伏惟执事亦所乐闻。而不以绞蔽为罪也。其言涉理气处。虽不及实体。犹虑穷深。领听不易。希音已绝。孤唱难谐。非执事不敢发。而又不能不咨且噫。此岂易言者哉。虽然以疑似不真之说。而惑世诬民。则之死不敢为也。况敢欺执事乎。更乞无以色物为眩。毕赐透察。而义在发明。不避僭踰。伏惟裁恕焉。
与公万世之义理。经天地之圣训。亦若可以与夺由我。抑扬在己。则事未中窾。义不明著。以虚心受宲疑。其势固然。弟亦莫知所以为执事善啚也。今此之云。惟申申以右之君子改之之义请教者。亶岂有他哉。此于理气师旨。皆有不可不辨者。而于执事。又不可不为同道之谋。所以卒不果于自同寒蝉吟而不言。而泣道由戚。嗃嗃为吉。同人之义。辞尚忠质。伏惟执事亦所乐闻。而不以绞蔽为罪也。其言涉理气处。虽不及实体。犹虑穷深。领听不易。希音已绝。孤唱难谐。非执事不敢发。而又不能不咨且噫。此岂易言者哉。虽然以疑似不真之说。而惑世诬民。则之死不敢为也。况敢欺执事乎。更乞无以色物为眩。毕赐透察。而义在发明。不避僭踰。伏惟裁恕焉。砥行此书。为圣学理气。不得不讲明。为先师旨义。不得不辨暴。为执事举措。不得不商禀。而书具踰时。日望庶几。迟回到此。如可得已。固贞于未发矣。但念风雷杳漠。日月征迈。南强不竞。转斡无期。又有朱子之谓较是二者。宁可见笑于今人之义。乃不敢终遂慎默之本心。而呈暴无隐。若其孺子之歌。犹为有无于心通。而原本彻终。前定不穷。则惟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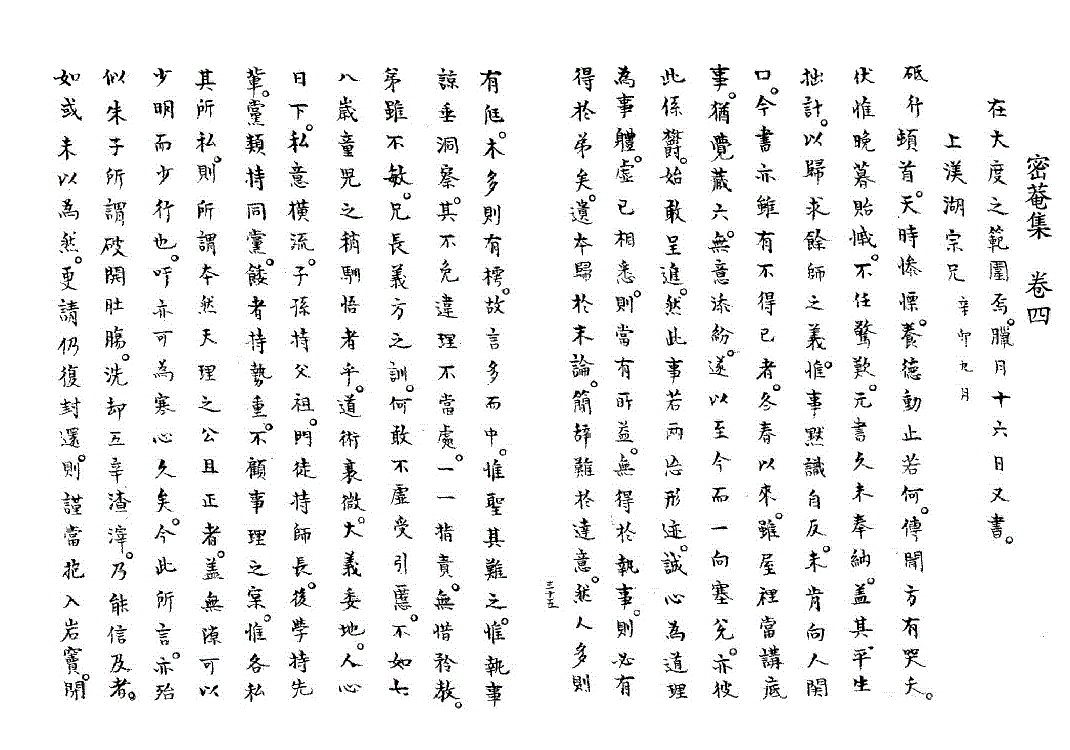 在大度之范围焉。腊月十六日又书。
在大度之范围焉。腊月十六日又书。上渼湖宗兄(辛卯九月)
砥行顿首。天时惨慄。养德动止若何。传闻方有哭夭。伏惟晚暮贻戚。不任惊叹。元书久未奉纳。盖其平生拙计。以归求馀师之义。惟事默识自反。未肯向人关口。今书亦虽有不得已者。冬春以来。虽屋里当讲底事。犹觉藏六。无意添纷。遂以至今而一向塞兑。亦彼此系郁。始敢呈进。然此事若两忘形迹。诚心为道理为事体。虚己相悉。则当有所益。无得于执事。则必有得于弟矣。遗本归于末论。简辞难于达意。然人多则有尪。木多则有樗。故言多而中。惟圣其难之。惟执事谅垂洞察。其不免违理不当处。一一指责。无惜矜教。弟虽不敏。兄长义方之训。何敢不虚受引慝。不如七八岁童儿之稍驯悟者乎。道术衰微。大义委地。人心日下。私意横流。子孙持父祖。门徒持师长。后学持先辈。党类持同党。喂者持势重。不顾事理之宲。惟各私其所私。则所谓本然天理之公且正者。盖无隙可以少明而少行也。吁亦可为寒心久矣。今此所言。亦殆似朱子所谓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及者。如或未以为然。更请仍复封还。则谨当抱入岩窦。闭
密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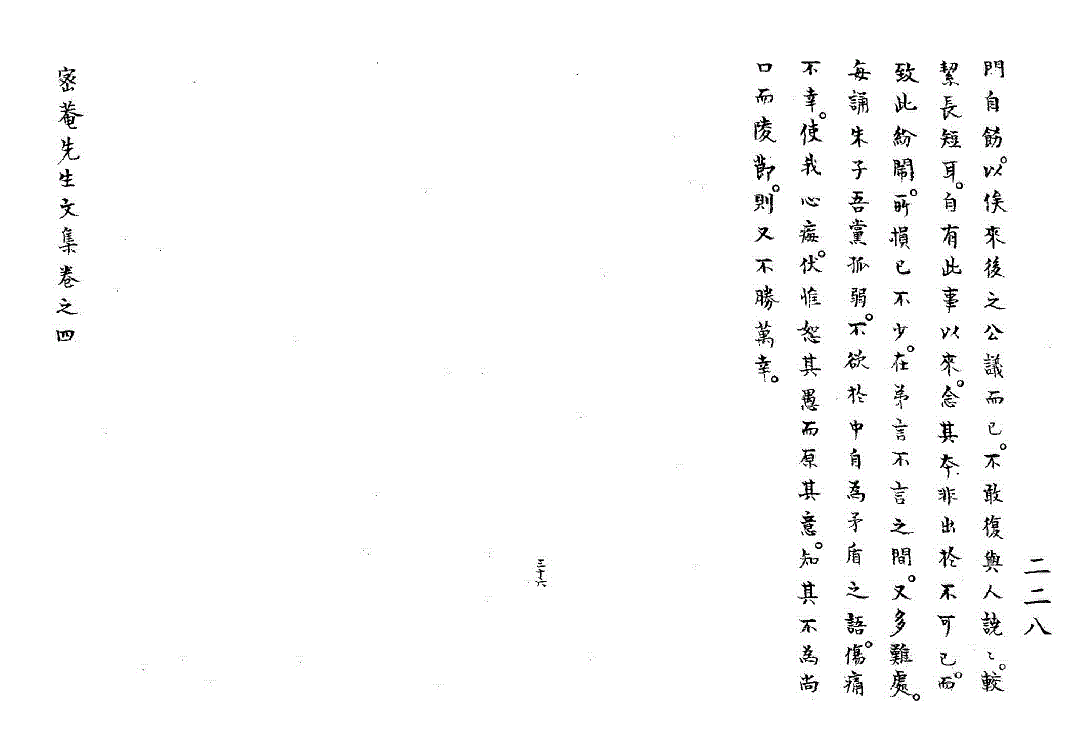 门自饬。以俟来后之公议而已。不敢复与人譊譊。较絜长短耳。自有此事以来。念其本非出于不可已。而致此纷闹。所损已不少。在弟言不言之间。又多难处。每诵朱子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之语。伤痛不幸。使我心痗。伏惟恕其愚而原其意。知其不为尚口而陵节。则又不胜万幸。
门自饬。以俟来后之公议而已。不敢复与人譊譊。较絜长短耳。自有此事以来。念其本非出于不可已。而致此纷闹。所损已不少。在弟言不言之间。又多难处。每诵朱子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之语。伤痛不幸。使我心痗。伏惟恕其愚而原其意。知其不为尚口而陵节。则又不胜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