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尼溪集卷之六 第 x 页
尼溪集卷之六
序
序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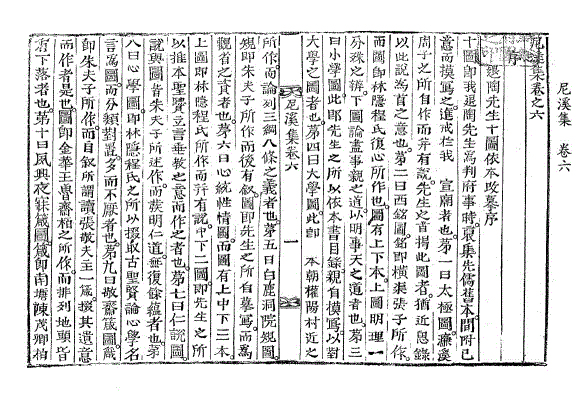 退陶先生十图依本改摹序
退陶先生十图依本改摹序十图即我退陶先生为判府事时。裒集先儒旧本。间附己意而摸写之。进戒于我 宣庙者也。第一曰太极图。濂溪周子之所自作而并有说。先生之首揭此图者。犹近思录以此说为首之意也。第二曰西铭图。铭即横渠张子所作。而图即林隐程氏复心所作也。图有上下本。上图明理一分殊之辨。下图论尽事亲之道。以明事天之道者也。第三曰小学图。此即先生之所以依本书目录。亲自模写。以对大学之图者也。第四曰大学图。此即 本朝权阳村近之所作。而论列三纲八条之义者也。第五曰白鹿洞院规图。规即朱夫子所作而后有叙。图即先生之所自摹写。而为观省之资者也。第六曰心统性情图。而图有上中下三本。上图即林隐程氏所作而并有说。中下二图。即先生之所以推本圣贤立言垂教之意而作之者也。第七曰仁说图。说与图皆朱夫子所述作。而发明仁道。无复馀蕴者也。第八曰心学图。即林隐程氏之所以掇取古圣贤论心学名言为图。而分类对置。多而不厌者也。第九曰敬斋箴图。箴即朱夫子所作。而自叙所谓读张敬夫主一箴。掇其遗意而作者是也。图即金华王鲁斋柏之所作。而排列地头皆有下落者也。第十曰夙兴夜寐箴图。箴即南塘陈茂卿柏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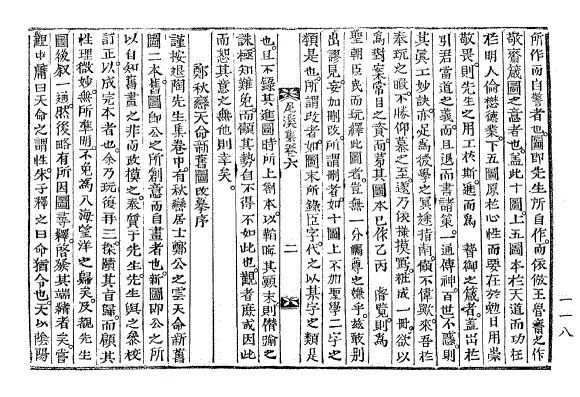 所作而自警者也。图即先生所自作。而依仿王鲁斋之作敬斋箴图之意者也。盖此十图。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于明人伦懋德业。下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于勉日用崇敬畏。则先生之用工于斯。进而为 亵御之箴者。盖出于引君当道之义。而且退而书诸策。一通传神。百世不惑。则其真工妙诀。亦足为后学之冥途指南。顾不伟欤。来吾于奉玩之暇。不胜仰慕之至。遂乃依㨾摸写。妆成一册。欲以为对案常目之资。而第其图本已作乙丙 睿览。则为 圣朝臣民而玩绎此图者。岂无一分触尊之嫌乎。玆敢别出谬见。妄加删改。所谓删者。如十图上不加圣学二字之类是也。所谓改者。如图末所录臣字。代之以某字之类是也。且不录其进图时所上劄本。以韬晦其颠末。则僭踰之诛。极知难免。而顾其势自不得不如此也。观者庶或因此而恕其意之无他则幸矣。
所作而自警者也。图即先生所自作。而依仿王鲁斋之作敬斋箴图之意者也。盖此十图。上五图本于天道而功在于明人伦懋德业。下五图原于心性而要在于勉日用崇敬畏。则先生之用工于斯。进而为 亵御之箴者。盖出于引君当道之义。而且退而书诸策。一通传神。百世不惑。则其真工妙诀。亦足为后学之冥途指南。顾不伟欤。来吾于奉玩之暇。不胜仰慕之至。遂乃依㨾摸写。妆成一册。欲以为对案常目之资。而第其图本已作乙丙 睿览。则为 圣朝臣民而玩绎此图者。岂无一分触尊之嫌乎。玆敢别出谬见。妄加删改。所谓删者。如十图上不加圣学二字之类是也。所谓改者。如图末所录臣字。代之以某字之类是也。且不录其进图时所上劄本。以韬晦其颠末。则僭踰之诛。极知难免。而顾其势自不得不如此也。观者庶或因此而恕其意之无他则幸矣。郑秋峦天命新旧图改摹序
谨按退陶先生集卷中。有秋峦居士郑公之云天命新旧图二本。旧图即公之所创意而自画者也。新图即公之所以自知旧画之非而改模之。奉质于先生。先生与之参校订正。以成完本者也。余乃玩复再三。探赜其旨归。而顾其性理微妙。无所准明。不免为入海望洋之归矣。及睹先生图后叙一通。然后略有所因图寻绎。启发其端绪者矣。尝观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朱子释之曰命犹令也。天以阴阳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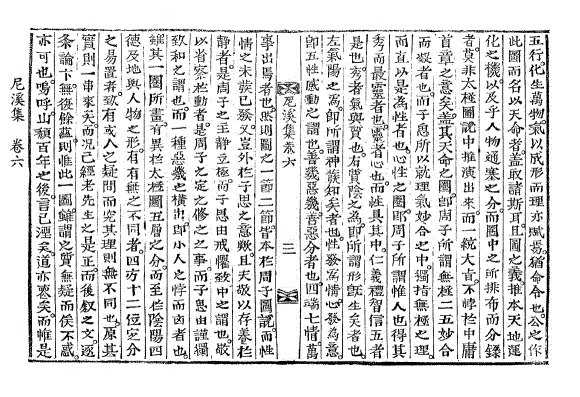 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公之作此图而名以天命者。盖取诸斯耳。且图之义。推本天地运化之机。以及乎人物通塞之分。而圈中之所排布而分录者。莫非太极图说中推演出来。而一统大旨。不悖于中庸首章之意矣。盖其天命之圈。即周子所谓无极二五妙合而凝者也。而子思所以就理气妙合之中。独指无极之理。而直以是为性者也。心性之圈。即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即所谓形既生矣者也。左气阳之为。即所谓神发知矣者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五性感动之谓也。善几恶几。善恶分者也。四端七情。万事出焉者也。然则图之一节二节。皆本于周子图说。而性情之未发已发。又岂外于子思之意欤。且夫敬以存养于静者。是周子之主静立极。而子思由戒惧致中之谓也。敬以省察于动者。是周子之定之修之之事。而子思由谨独致和之谓也。而一种恶几之横出。即小人之悖而凶者也。虽其一圈所画。有异于太极图五层之分。而至于阴阳四德及地与人物之形。有有无之不同者。四方十二位定分之易置者。致有或人之疑问而究其理则无不同也。原其实则一串来矣。而况已经老先生之是正。而后叙之文。逐条论卞。无复馀蕴。则惟此一图。虽谓之质无疑而俟不惑。亦可也。呜呼。山颓百年之后。言已湮矣。道亦丧矣。而惟是
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公之作此图而名以天命者。盖取诸斯耳。且图之义。推本天地运化之机。以及乎人物通塞之分。而圈中之所排布而分录者。莫非太极图说中推演出来。而一统大旨。不悖于中庸首章之意矣。盖其天命之圈。即周子所谓无极二五妙合而凝者也。而子思所以就理气妙合之中。独指无极之理。而直以是为性者也。心性之圈。即周子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者也。灵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气与质也。右质阴之为。即所谓形既生矣者也。左气阳之为。即所谓神发知矣者也。性发为情。心发为意。即五性感动之谓也。善几恶几。善恶分者也。四端七情。万事出焉者也。然则图之一节二节。皆本于周子图说。而性情之未发已发。又岂外于子思之意欤。且夫敬以存养于静者。是周子之主静立极。而子思由戒惧致中之谓也。敬以省察于动者。是周子之定之修之之事。而子思由谨独致和之谓也。而一种恶几之横出。即小人之悖而凶者也。虽其一圈所画。有异于太极图五层之分。而至于阴阳四德及地与人物之形。有有无之不同者。四方十二位定分之易置者。致有或人之疑问而究其理则无不同也。原其实则一串来矣。而况已经老先生之是正。而后叙之文。逐条论卞。无复馀蕴。则惟此一图。虽谓之质无疑而俟不惑。亦可也。呜呼。山颓百年之后。言已湮矣。道亦丧矣。而惟是尼溪集卷之六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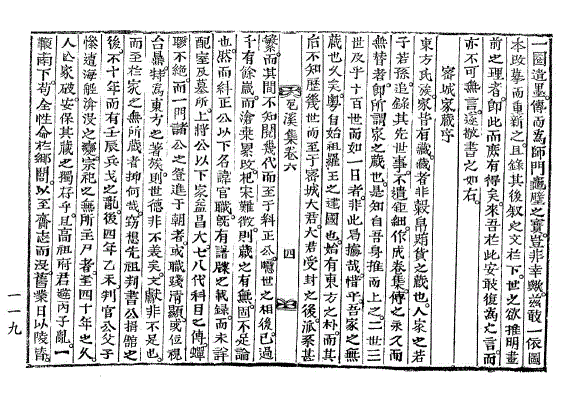 一圈遗墨。传而为师门龟璧之宝。岂非幸欤。玆敢一依图本改摹而重新之。且录其后叙之文于下。世之欲推明画前之理者。即此而庶有得矣。来吾于此安敢复为之言。而亦不可无言。遂敬书之如右。
一圈遗墨。传而为师门龟璧之宝。岂非幸欤。玆敢一依图本改摹而重新之。且录其后叙之文于下。世之欲推明画前之理者。即此而庶有得矣。来吾于此安敢复为之言。而亦不可无言。遂敬书之如右。密城家藏序
东方氏族。家皆有藏。藏者非谷帛贿货之藏也。人家之若子若孙。追录其先世事。不遗钜细。作成卷集。传之永久而无替者。即所谓家之藏也。是知自吾身推而上之。二世三世及乎十百世而如一日者。非此曷据哉。惜乎。吾家之无藏也久矣。粤自始祖罗王之建国也。始有东方之朴。而其后不知历几世而至于密城大君。大君受封之后。派系甚繁。而其间不知阅几代而至于纠正公。噫世之相后。已过千有馀岁。而沧桑累改。杞宋难徵。则藏之有无。固不足论也。然而纠正公以下名讳官职。既有谱牒之载录。而未详配室及墓所。上将公以下家益昌大。七八代科目之传。蝉联不绝。而一门诸公之登进于朝者。或职践清显。或位视台鼎。特为东方之著族。则世德非不美矣。文献非不足也。而至于家之无所藏者抑何哉。窃想先祖判书公捐馆之后。不十年而有壬辰兵戈之乱。后四年乙未。判官公父子惨遭海船渰没之变。宗祀之无所主尸者。至四十年之久。人亡家破。安保其藏之独存乎。且高祖府君避丙子乱。一鞭南下。苟全性命于乡闾。以至赍志而没。旧业日以陵替。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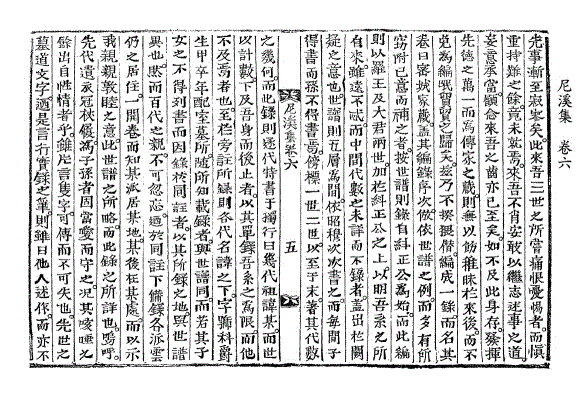 先事渐至寂寥矣。此来吾三世之所尝痛恨忧惕者。而慎重持难之馀。竟未就焉。来吾不肖安敢以继志述事之道。妄意承当。顾念来吾之齿亦已至矣。如不及此身存。发挥先德之万一而为传家之藏。则无以饬稚昧于来后。而不免为编氓贸贸之归矣。玆乃不揆猥僭。编成一录。而名其卷曰密城家藏。盖其编录序次。仿依世谱之例。而多有所窃附己意而补之者。按世谱则录自纠正公为始。而此编则以罗王及大君两世。加于纠正公之上。以明吾系之所自来。虽远不忒。而中间代数之未详而不录者。盖出于阙疑之意也。世谱则五层为间。依昭穆次次书之。而每间子得书而孙不得书焉。傍标一世二世。以至于末。著其代数之几何。而此录则逐代特书于独行曰几代祖讳某。而世以计数。下及吾身而后止者。以其单录吾系之为限。而他不及焉者也。至于旁注所录则各代名讳之下。字号科爵生甲卒年配室墓所。随所知载录者。与世谱同。而若其子女之不得列书而因录于同注者。以其所录之地。与世谱异也。然而百代之亲。不可忽忘。乃于同注下备录各派云仍之居住。一开卷而知某派居某地。某后在某处。而以示我亲亲敦睦之意。此世谱之所略。而此录之所详也。呜呼。先代遗衣冠杖履。为子孙者固当爱而守之。况其咳唾之馀出自性情者乎。虽片言只字。可传而不可失也。先世之墓道文字。乃是言行实录之笔。则虽曰他人述作。而亦不
先事渐至寂寥矣。此来吾三世之所尝痛恨忧惕者。而慎重持难之馀。竟未就焉。来吾不肖安敢以继志述事之道。妄意承当。顾念来吾之齿亦已至矣。如不及此身存。发挥先德之万一而为传家之藏。则无以饬稚昧于来后。而不免为编氓贸贸之归矣。玆乃不揆猥僭。编成一录。而名其卷曰密城家藏。盖其编录序次。仿依世谱之例。而多有所窃附己意而补之者。按世谱则录自纠正公为始。而此编则以罗王及大君两世。加于纠正公之上。以明吾系之所自来。虽远不忒。而中间代数之未详而不录者。盖出于阙疑之意也。世谱则五层为间。依昭穆次次书之。而每间子得书而孙不得书焉。傍标一世二世。以至于末。著其代数之几何。而此录则逐代特书于独行曰几代祖讳某。而世以计数。下及吾身而后止者。以其单录吾系之为限。而他不及焉者也。至于旁注所录则各代名讳之下。字号科爵生甲卒年配室墓所。随所知载录者。与世谱同。而若其子女之不得列书而因录于同注者。以其所录之地。与世谱异也。然而百代之亲。不可忽忘。乃于同注下备录各派云仍之居住。一开卷而知某派居某地。某后在某处。而以示我亲亲敦睦之意。此世谱之所略。而此录之所详也。呜呼。先代遗衣冠杖履。为子孙者固当爱而守之。况其咳唾之馀出自性情者乎。虽片言只字。可传而不可失也。先世之墓道文字。乃是言行实录之笔。则虽曰他人述作。而亦不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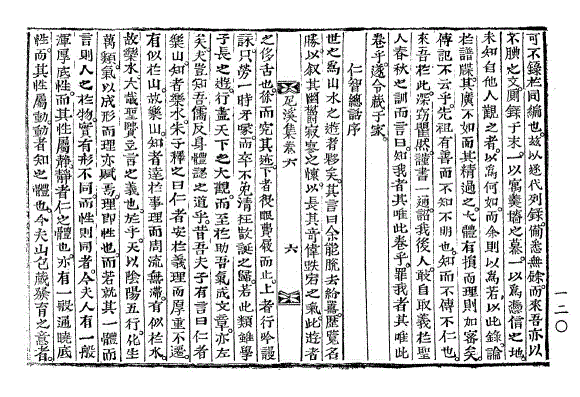 可不录于同编也。玆以逐代列录。备悉无馀。而来吾亦以不腆之文。厕录于末。一以寓羹墙之慕。一以为凭信之地。未知自他人观之者。以为何如。而余则以为若以此录。论于谱牒。其广不如而其精过之。大体有损而理则加密矣。传记不云乎。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来吾于此。深窃瞿然。谨书一通。诏我后人。敢自取义于圣人春秋之训而言曰。知我者其唯此卷乎。罪我者其唯此卷乎。遂令藏于家。
可不录于同编也。玆以逐代列录。备悉无馀。而来吾亦以不腆之文。厕录于末。一以寓羹墙之慕。一以为凭信之地。未知自他人观之者。以为何如。而余则以为若以此录。论于谱牒。其广不如而其精过之。大体有损而理则加密矣。传记不云乎。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来吾于此。深窃瞿然。谨书一通。诏我后人。敢自取义于圣人春秋之训而言曰。知我者其唯此卷乎。罪我者其唯此卷乎。遂令藏于家。仁智总话序
世之为山水之游者夥矣。其言曰余能脱去纷嚣。历览名胜。以叙其幽郁寂寥之怀。以长其奇伟跌宕之气。此游者之侈舌也。徐而究其迹。下者役眼费屐而止。上者行吟谩咏。只劳一时牙喙。而卒不免清狂散诞之归。若此类虽学子长之游。行尽天下之大观。而至于助吾气成文章。亦左矣。夫岂知吾儒反身体认之道乎。昔吾夫子有言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朱子释之曰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大哉圣贤立言之义也。于乎。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类。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理即性也。而若就其一体而言则人之于物。实有形不同。而性则同者。今夫人有一般浑厚底性。而其性属静。静者仁之体也。亦有一般通晓底性。而其性属动。动者知之体也。今夫山包藏发育之意者。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1H 页
 是动也。而至于一气磅礴。安重不迁。则其体主于静。今夫水含畜渊深之源者。是静也。而及其滔滔而流。日夜不息。则其体主于动。然则仁者之乐山。以其心之浑厚安重。不为外物之所移者。与山同故也。知者之乐水。以其心之周流委曲。未尝或滞于一隅者。与水同故也。虽然仁者之静。非块然死守之谓也。其所以见得天地间。百事万理。皆在吾心。无不相关。则其静也固未尝不动。而山之体主于静。而静中有动者似之。知者之动。非劳攘烦扰之谓也。其所以见得许多道理分明。行其所无事。而其理甚简。则其动也亦未尝不静。而水之体主于动。而动中有静者似之。夫如是则夫子之以动静二字。形容仁知之体。而末乃以乐寿二字。明言仁知之效者。盖言其一体之如是。而其理则无不同也。岂非所谓浑然天理。兼尽仁智之全体者乎。顾余末学。识蔑业浅。安敢以管窥之见。妄论仁智之说哉。惟其十年咿唔之馀。偶作山水之行。是行也非直为景物役也。于山而见其有静之体则曰仁者而后乐此。不仁者虽见此不乐也。于水而见其有动之体则曰知者而后乐此。不知者虽见此不乐也。心有感发。欣然而归。因著纪行录一通。敢自取义于夫子之训。而名其卷曰仁智总话。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窃自念人之所禀于天者。莫不皆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其端有四。亦莫不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而其目有七。是知性情咸统于心。而心亦有静有动。故
是动也。而至于一气磅礴。安重不迁。则其体主于静。今夫水含畜渊深之源者。是静也。而及其滔滔而流。日夜不息。则其体主于动。然则仁者之乐山。以其心之浑厚安重。不为外物之所移者。与山同故也。知者之乐水。以其心之周流委曲。未尝或滞于一隅者。与水同故也。虽然仁者之静。非块然死守之谓也。其所以见得天地间。百事万理。皆在吾心。无不相关。则其静也固未尝不动。而山之体主于静。而静中有动者似之。知者之动。非劳攘烦扰之谓也。其所以见得许多道理分明。行其所无事。而其理甚简。则其动也亦未尝不静。而水之体主于动。而动中有静者似之。夫如是则夫子之以动静二字。形容仁知之体。而末乃以乐寿二字。明言仁知之效者。盖言其一体之如是。而其理则无不同也。岂非所谓浑然天理。兼尽仁智之全体者乎。顾余末学。识蔑业浅。安敢以管窥之见。妄论仁智之说哉。惟其十年咿唔之馀。偶作山水之行。是行也非直为景物役也。于山而见其有静之体则曰仁者而后乐此。不仁者虽见此不乐也。于水而见其有动之体则曰知者而后乐此。不知者虽见此不乐也。心有感发。欣然而归。因著纪行录一通。敢自取义于夫子之训。而名其卷曰仁智总话。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窃自念人之所禀于天者。莫不皆有仁义礼智之性而其端有四。亦莫不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而其目有七。是知性情咸统于心。而心亦有静有动。故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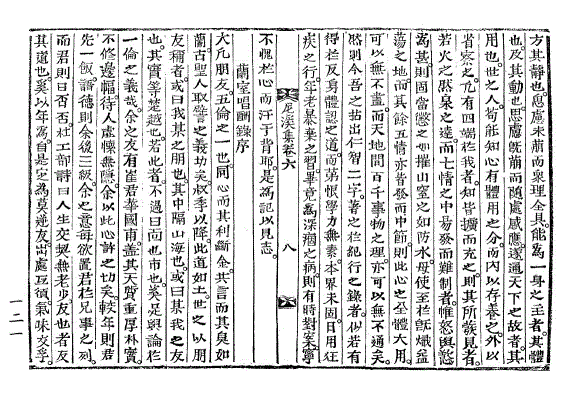 方其静也。思虑未萌而众理全具。能为一身之主者。其体也。及其动也。思虑既萌而随处感应。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世之人。苟能知心有体用之分。而内以存养之。外以省察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则其所发见者。若火之然泉之达。而七情之中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与欲为甚。则固当惩之如摧山窒之如防水。毋使至于既炽益荡之地。而其馀五情亦皆发而中节。则此心之全体大用。可以无不尽。而天地间百千事物之理。亦可以无不通矣。然则今吾之拈出仁智二字。著之于纪行之录者。似若有得于反身体认之道。而第恨学力无素。本界未固。日用狂疾之行。年老暴弃之习。毕竟为深痼之病。则有时对案。宁不愧于心而汗于背耶。是为记以见志。
方其静也。思虑未萌而众理全具。能为一身之主者。其体也。及其动也。思虑既萌而随处感应。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世之人。苟能知心有体用之分。而内以存养之。外以省察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则其所发见者。若火之然泉之达。而七情之中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与欲为甚。则固当惩之如摧山窒之如防水。毋使至于既炽益荡之地。而其馀五情亦皆发而中节。则此心之全体大用。可以无不尽。而天地间百千事物之理。亦可以无不通矣。然则今吾之拈出仁智二字。著之于纪行之录者。似若有得于反身体认之道。而第恨学力无素。本界未固。日用狂疾之行。年老暴弃之习。毕竟为深痼之病。则有时对案。宁不愧于心而汗于背耶。是为记以见志。兰室唱酬录序
大凡朋友。五伦之一也。同心而其利断金。共言而其臭如兰。古圣人取譬之义切矣。叔季以降。此道如土。世之以朋友称者。或曰我某之朋也。其中隔山海也。或曰某我之友也。其实等楚越也。若此者。不过曰面也市也。奚足与论于一伦之义哉。余之友有崔君华国甫。盖其天质重厚朴实。不修边幅。待人虚怀无隐。余以此心许之切矣。较年则君先一饭。语德则余后三级。余之意每欲置君于兄事之列。而君则曰否否。杜工部诗曰人生交契无老少。友也者反其道也。奚以年为。自是定为莫逆友。出处互须。气味交孚。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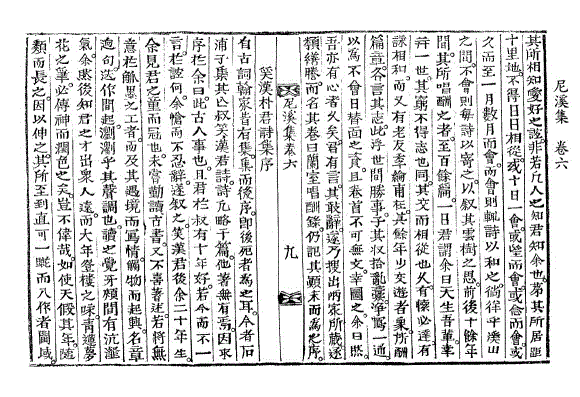 其所相知爱好之谊。非若凡人之知君知余也。第其所居距十里地。不得日日相从。或十日一会。或望而会。或念而会。或久而至一月数月而会。而会则辄诗以和之。徜徉乎溪山之间。不会则每诗以寄之。以叙其云树之思。前后十馀年间。其所唱酬之者。至百馀篇。一日君谓余曰天生吾辈。幸并一世。其穷不得志也同。其交而相从也久。有怀必达。有咏相和。而又有老友季纶甫在。其馀年少交游者众。所酬篇章。各言其志。此浮世间胜事。子其收拾乱藁。净写一通。以为不会日替面之资。且卷首不可无文。幸图之。余曰然。吾亦有心者久矣。君有言。其敢辞。遂乃搜出两家所藏。逐类缮誊。而名其卷曰兰室唱酬录。仍记其颠末而为之序。
其所相知爱好之谊。非若凡人之知君知余也。第其所居距十里地。不得日日相从。或十日一会。或望而会。或念而会。或久而至一月数月而会。而会则辄诗以和之。徜徉乎溪山之间。不会则每诗以寄之。以叙其云树之思。前后十馀年间。其所唱酬之者。至百馀篇。一日君谓余曰天生吾辈。幸并一世。其穷不得志也同。其交而相从也久。有怀必达。有咏相和。而又有老友季纶甫在。其馀年少交游者众。所酬篇章。各言其志。此浮世间胜事。子其收拾乱藁。净写一通。以为不会日替面之资。且卷首不可无文。幸图之。余曰然。吾亦有心者久矣。君有言。其敢辞。遂乃搜出两家所藏。逐类缮誊。而名其卷曰兰室唱酬录。仍记其颠末而为之序。笑汉朴君诗集序
自古词翰家皆有集。集而后序。即后死者为之耳。今者石浦子集其亡叔笑汉君诗。诗凡略干篇。他著无有焉。因求序于余曰。此古人事也。且君于叔有十年好。若今而不一言。于谊何。余怆而不忍辞。遂叙之。笑汉君后余二十年生。余见君之童而冠也。未尝勤读古书。又不喜著述。若将无意于觚墨之工者。而及其遇境而写情。触物而起兴。名章迥句。迭作间起。浏浏乎其声调也。读之觉牙颊间有沆瀣气。余然后知君之才出众人远。而大年登楼之咏。青莲梦花之笔。必传神而润色之矣。岂不伟哉。如使天假其年。随类而长之。因以伸之。其所至到直可一蹴而入作者阃域。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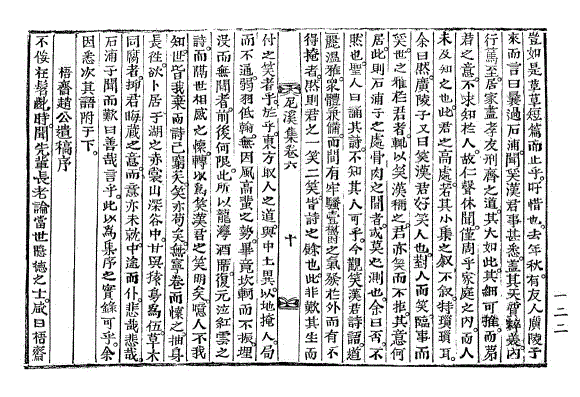 岂如是草草短篇而止乎。吁惜也。去年秋。有友人广陵子来而言曰曩过石浦。闻笑汉君事甚悉。盖其天质粹美。内行笃至。居家尽孝友刑齐之道。其大如此。其细可推。而第君之意。不求知于人。故仁声休闻。仅周乎家庭之内。而人未及知之也。此君之高处。若其小集之叙不叙。特琐琐耳。余曰然。广陵子又曰笑汉君好笑人也。对人而笑。临事而笑。世之雅于君者。辄以笑汉称之。君亦笑而不拒。其意何居。此则石浦子之处骨肉之间者。或莫之测也。余曰否。不然也。圣人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今观笑汉君诗语。遒丽温雅。众体兼备。而间有牢骚壹郁之气发于外而有不得掩者。然则君之一笑二笑。皆诗之馀也。此非叹其生而付之笑者乎。于乎。东方取人之道。与中土异。以地掩人。局而不通。弱羽低翰。无因风高蜚之势。毕竟坎轲而不振。埋没而无闻者。前后何限。此所以龙湾酒席。复元泣红云之诗。而隔世相感之怀。转以为笑汉君之笑明矣。噫人不我知。世皆我弃而诗已穷矣。笑亦苟矣。无宁卷而怀之。抽身长往。欲卜居于湖之赤裳山深谷中。甘与猿鸟为伍。草木同腐者。抑君晦藏之意。而意亦未就。中途而仆。悲哉悲哉。石浦子闻而叹曰善哉言乎。此以为集序之实录可乎。余因悉次其语附于下。
岂如是草草短篇而止乎。吁惜也。去年秋。有友人广陵子来而言曰曩过石浦。闻笑汉君事甚悉。盖其天质粹美。内行笃至。居家尽孝友刑齐之道。其大如此。其细可推。而第君之意。不求知于人。故仁声休闻。仅周乎家庭之内。而人未及知之也。此君之高处。若其小集之叙不叙。特琐琐耳。余曰然。广陵子又曰笑汉君好笑人也。对人而笑。临事而笑。世之雅于君者。辄以笑汉称之。君亦笑而不拒。其意何居。此则石浦子之处骨肉之间者。或莫之测也。余曰否。不然也。圣人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今观笑汉君诗语。遒丽温雅。众体兼备。而间有牢骚壹郁之气发于外而有不得掩者。然则君之一笑二笑。皆诗之馀也。此非叹其生而付之笑者乎。于乎。东方取人之道。与中土异。以地掩人。局而不通。弱羽低翰。无因风高蜚之势。毕竟坎轲而不振。埋没而无闻者。前后何限。此所以龙湾酒席。复元泣红云之诗。而隔世相感之怀。转以为笑汉君之笑明矣。噫人不我知。世皆我弃而诗已穷矣。笑亦苟矣。无宁卷而怀之。抽身长往。欲卜居于湖之赤裳山深谷中。甘与猿鸟为伍。草木同腐者。抑君晦藏之意。而意亦未就。中途而仆。悲哉悲哉。石浦子闻而叹曰善哉言乎。此以为集序之实录可乎。余因悉次其语附于下。梧斋赵公遗稿序
不佞在髫龀时。闻先辈长老论当世隐德之士。咸曰梧斋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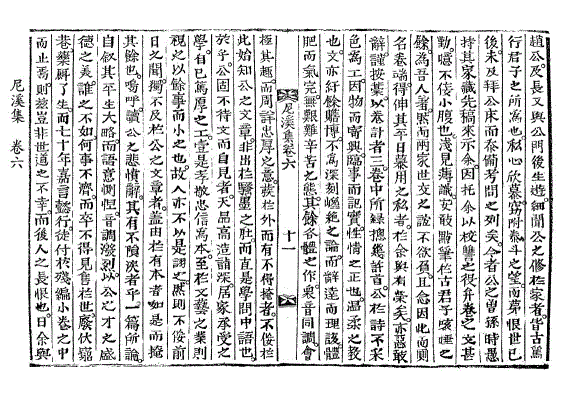 赵公。及长又与公门后生游。细闻公之修于家者。皆古笃行君子之所为也。私心欣慕。窃附泰斗之望。而第恨世已后。未及拜公床而忝备考问之列矣。今者公之曾孙时愚持其家藏先稿来示余。因托余以校雠之役弁卷之文甚勤。噫不佞小腹也。浅见薄识。安敢点笔于古君子咳唾之馀。为吾人羞。然而两家世交之谊不欲负。且念因此而厕名卷端。得伸其平日慕用之私者。于余与有荣矣。亦恶敢辞。谨按藁。以卷计者三。卷中所录总几许首。公于诗不采色为工。因物而寄兴。临事而记实。性情之正也。温柔之教也。文亦纡馀赡博。不为深刻巉绝之论。而辞达而理该。体肥而气完。无艰难辛苦之态。其馀各体之作。众音同调。会极其趣。而周详忠厚之意。发于外而有不得掩者。不佞于此始知公之文章。非出于骚墨之肚。而直是学问中语也。于乎。公固不待文而自见者。天品高造诣深。居家承受之学。自己笃厚之工。壹是孝敬忠信为本。至于文艺之业则视之以馀事而小之也。故人亦不以是诩之。然则不佞前日之闻。独不及于公之文章者。盖由于有本者如是而掩其馀也。呜呼。读公之悲愤辞。其有不陨泪者乎。一篇所论。自叙其平生大略。而语意恻怛。音调激烈。以公之才之盛德之美。谁之不如。何事不济。而卒不得见售于世。废伏穷巷。药饵了生。而七十年嘉言懿行。徒付于残编小卷之中而止焉。则玆岂非世道之不幸。而后人之长恨也。日余与
赵公。及长又与公门后生游。细闻公之修于家者。皆古笃行君子之所为也。私心欣慕。窃附泰斗之望。而第恨世已后。未及拜公床而忝备考问之列矣。今者公之曾孙时愚持其家藏先稿来示余。因托余以校雠之役弁卷之文甚勤。噫不佞小腹也。浅见薄识。安敢点笔于古君子咳唾之馀。为吾人羞。然而两家世交之谊不欲负。且念因此而厕名卷端。得伸其平日慕用之私者。于余与有荣矣。亦恶敢辞。谨按藁。以卷计者三。卷中所录总几许首。公于诗不采色为工。因物而寄兴。临事而记实。性情之正也。温柔之教也。文亦纡馀赡博。不为深刻巉绝之论。而辞达而理该。体肥而气完。无艰难辛苦之态。其馀各体之作。众音同调。会极其趣。而周详忠厚之意。发于外而有不得掩者。不佞于此始知公之文章。非出于骚墨之肚。而直是学问中语也。于乎。公固不待文而自见者。天品高造诣深。居家承受之学。自己笃厚之工。壹是孝敬忠信为本。至于文艺之业则视之以馀事而小之也。故人亦不以是诩之。然则不佞前日之闻。独不及于公之文章者。盖由于有本者如是而掩其馀也。呜呼。读公之悲愤辞。其有不陨泪者乎。一篇所论。自叙其平生大略。而语意恻怛。音调激烈。以公之才之盛德之美。谁之不如。何事不济。而卒不得见售于世。废伏穷巷。药饵了生。而七十年嘉言懿行。徒付于残编小卷之中而止焉。则玆岂非世道之不幸。而后人之长恨也。日余与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3L 页
 夏山成君涉入梧山中。梧即公旧所也。到今池台废坏。草树荒芜。抚古周览。乌得无伤感之怀乎。忽植杖不歌而叹曰硕人已去。吾将安放。山高水长。清风不沫。古人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欤。今余之适会来斯。数日盘旋。疑若有所导者存。况余方有所受托于公之子孙者。及此时卒业成美。以彰公之隐德。不亦可乎。成君曰子之言然。遂盥手而书。
夏山成君涉入梧山中。梧即公旧所也。到今池台废坏。草树荒芜。抚古周览。乌得无伤感之怀乎。忽植杖不歌而叹曰硕人已去。吾将安放。山高水长。清风不沫。古人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欤。今余之适会来斯。数日盘旋。疑若有所导者存。况余方有所受托于公之子孙者。及此时卒业成美。以彰公之隐德。不亦可乎。成君曰子之言然。遂盥手而书。痴轩河公(应命)遗稿序
不佞弱冠。拜忍斋公床下。公赐之坐。因言两家姻亲之谊。年少人持身涉世之道甚悉。其所谆谆然命之者。即古君子厚德之风。不佞心窃佩服而归矣。后从公之仲子痴轩公游。讲世好深且久。盖痴轩公之于不佞。齿发有差。而其不挟长不少少之心无间焉。如是四十馀年。不幸而有存殁之感。悲哉。今者公之子复浩甫。持其家藏先稿示余。因求叙而言曰。窃观世之以此等事付嘱于人者。必先于深知分厚之间。则今余之不走当世工言之君子。而于执事者。意有在也。盖此卷集。即先君子晚年所就。而若有共和者。必书其人著述与其名号。一体收录而成。则合卷所录。本稿不过三之一。无多也。昔年梅隐堂唱酬之篇。俱在卷中。而执事之名。亦屡书不一书。此非执事之尤所感发而必置一言其间者乎。不佞作而对曰唯唯。君之意诚是矣。不佞虽雕篆之不足。敢不竭吾有。以塞君之厚望乎。尝闻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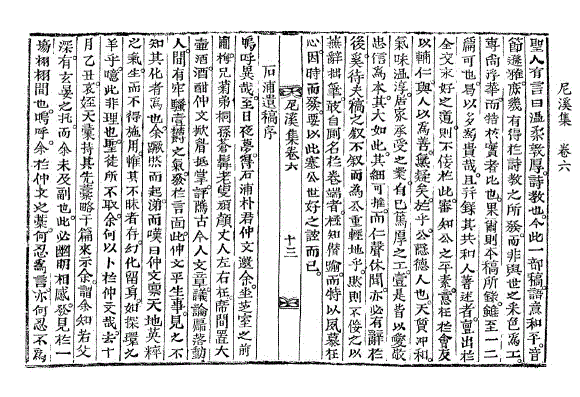 圣人有言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今此一部稿。语意和平。音节逊雅。庶几有得于诗教之所发。而非与世之采色为工。专尚浮华。而牿于实者比也。果尔则本稿所录。虽至一二篇可也。曷以多为贵哉。且并录其共和人著述者。亶出于全交永好之道。则不佞于此。审知公之平素。意在于会友以辅仁。与人以为善。无疑矣。于乎。公隐德人也。天质冲和。气味温淳。居家承受之业。自己笃厚之工。壹是皆以爱敬忠信为本。其大如此。其细可推。而仁声休闻。亦必有辞于后。奚待夫稿之叙不叙而为公重轻地乎。然则不佞之以芜辞拙笔。敢自厕名于卷端者。极知僭踰。而特以夙慕在心。因时而发。要以此塞公世好之谊而已。
圣人有言曰温柔敦厚。诗教也。今此一部稿。语意和平。音节逊雅。庶几有得于诗教之所发。而非与世之采色为工。专尚浮华。而牿于实者比也。果尔则本稿所录。虽至一二篇可也。曷以多为贵哉。且并录其共和人著述者。亶出于全交永好之道。则不佞于此。审知公之平素。意在于会友以辅仁。与人以为善。无疑矣。于乎。公隐德人也。天质冲和。气味温淳。居家承受之业。自己笃厚之工。壹是皆以爱敬忠信为本。其大如此。其细可推。而仁声休闻。亦必有辞于后。奚待夫稿之叙不叙而为公重轻地乎。然则不佞之以芜辞拙笔。敢自厕名于卷端者。极知僭踰。而特以夙慕在心。因时而发。要以此塞公世好之谊而已。石浦遗稿序
呜呼异哉。至日夜梦。得石浦朴君仲文邀余。坐芝室之前圃。梅兄菊弟桐孙苍髯老叟顽颜丈人左右在。席间置大壶酒。酒酣仲文掀眉抵掌。评骘古今人文章。议论磊落动人。间有牢骚壹郁之气。发于言面。此仲文平生事。见之不知其化者为也。余蹶然而起。涕而叹曰仲文禀天地英粹之气。生而不得施用。惟其不昧者存。幻化留身。如探环之羊乎。噫此非理也。圣徒所不取。余何以卜于仲文哉。去十月乙丑。哀侄天汇持其先藁略干篇来示余。谓余知若父深。有玄晏之托。而余未及副也。此必幽明相感。发见于一场栩栩间也。呜呼。余于仲文之藁。何忍为言。亦何忍不为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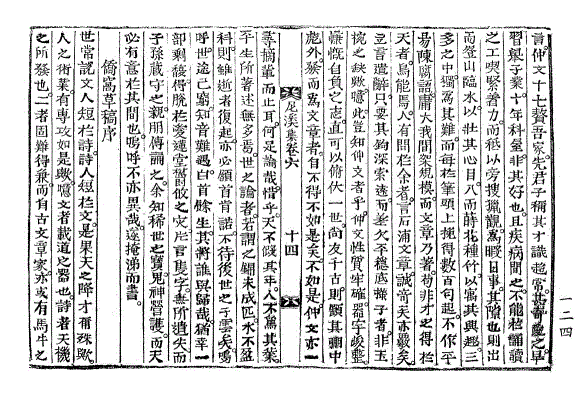 言。仲文十七赘吾家。先君子称其才识超常。甚奇爱之。早习举子业。十年科屋。非其好也。且疾病间之。不能于诵读之工吃紧着力。而秪以旁搜猎观。为暇日事。其隙也则出而登山临水。以壮其心目。入而莳花种竹。以寓其兴趣。三多之中。独为其难。而每于笔头上挽得数百匀起。不作平易陈腐语。庸大我间架规模。而文章乃著。苟非才之得于天者。乌能焉。人有问于余者。言石浦文章。诚奇矣亦覈矣。立言遣辞。只要其钩深索远。而差欠平稳底㨾子者。非玉碗之缺欤。噫。此岂知仲文者乎。仲文性质牢确。器宇峻整。慷慨自负之志。直可以俯伏一世。尚友千古。则顾其弸中彪外。发而为文章者。自不得不如是矣。不如是。仲文亦一寻摘辈而止耳。何足论哉。惜乎。天不假其年。人不笃其业。平生所著述无多焉。世之论者。若谓之锦未成匹。水不盈科。则虽逝者复起。亦必颔首肯诺。不待后世之子云矣。呜呼。世途已穷。知音难遇。白首馀生。其将谁与归哉。犹幸一部剩馥。得脱于爱莲堂郁攸之灾。片言只字。无所遗失。而子孙藏守之。亲朋传诵之。余知稀世之宝。鬼神营护。而天必有意于其间也。呜呼不亦异哉。遂掩涕而书。
言。仲文十七赘吾家。先君子称其才识超常。甚奇爱之。早习举子业。十年科屋。非其好也。且疾病间之。不能于诵读之工吃紧着力。而秪以旁搜猎观。为暇日事。其隙也则出而登山临水。以壮其心目。入而莳花种竹。以寓其兴趣。三多之中。独为其难。而每于笔头上挽得数百匀起。不作平易陈腐语。庸大我间架规模。而文章乃著。苟非才之得于天者。乌能焉。人有问于余者。言石浦文章。诚奇矣亦覈矣。立言遣辞。只要其钩深索远。而差欠平稳底㨾子者。非玉碗之缺欤。噫。此岂知仲文者乎。仲文性质牢确。器宇峻整。慷慨自负之志。直可以俯伏一世。尚友千古。则顾其弸中彪外。发而为文章者。自不得不如是矣。不如是。仲文亦一寻摘辈而止耳。何足论哉。惜乎。天不假其年。人不笃其业。平生所著述无多焉。世之论者。若谓之锦未成匹。水不盈科。则虽逝者复起。亦必颔首肯诺。不待后世之子云矣。呜呼。世途已穷。知音难遇。白首馀生。其将谁与归哉。犹幸一部剩馥。得脱于爱莲堂郁攸之灾。片言只字。无所遗失。而子孙藏守之。亲朋传诵之。余知稀世之宝。鬼神营护。而天必有意于其间也。呜呼不亦异哉。遂掩涕而书。侨窝草稿序
世常说文人短于诗。诗人短于文。是果天之降才尔殊欤。人之术业。有专攻如是欤。噫文者载道之器也。诗者天机之所发也。二者固难得兼。而自古文章家。亦或有马牛之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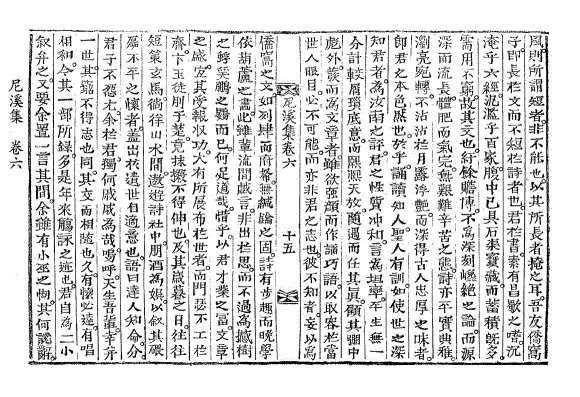 风。则所谓短者。非不能也。以其所长者掩之耳。吾友侨窝子。即长于文而不短于诗者也。君于书。素有昌歜之嗜。沉淹乎六经。汎滥乎百家。腹中已具石渠宝藏。而蓄积既多。需用不穷。故其文也。纡馀赡博。不为深刻巉绝之论。而源深而流长。体肥而气完。无艰难辛苦之态。诗亦平实典雅。浏亮宛转。不沾沾于月露浮艳。而深得古人忠厚之味者。即君之本色然也。于乎。诵读知人。圣人有训。如使世之深知君者。为汝南之评。君之性质冲和。言为坦率。平生无一分计较屑琐底意。而熙熙天放。随遇而任其真。顾其弸中彪外。发而为文章者。虽欲强颜而作谄巧语。以取容于当世人眼目。必不可能。而亦非君之志也。彼不知者。妄以为侨窝之文。如列肆而府帑。无缄钥之固。诗有步趣而晚学依葫芦之画。此虽辈流间戏言。非出于思。而不过为撼树之蜉笑鹏之鴳而已。何足道哉。惜乎。以君才业之富。文章之盛。宜其受报收功。大有所展布于世者。而门瑟不工于齐。卞玉徒刖于楚。竟抹摋不得伸也。及其岁暮之日。往往短策玄马。徜徉山水间。遨游诗社中。朋酒为娱。以叙其碨磊不平之怀者。盖出于遗世自适意也。语曰达人知命。分。君子不怨尤。余于君。独何戚戚为哉。呜呼。天生吾辈。幸并一世。其穷不得志也同。其交而相随也久。有怀必达。有唱相和。今其一部所录。多是年来觞咏之迹也。君自为二小叙弁之。又要余置一言其间。余虽有小巫之㥘。其何说辞。
风。则所谓短者。非不能也。以其所长者掩之耳。吾友侨窝子。即长于文而不短于诗者也。君于书。素有昌歜之嗜。沉淹乎六经。汎滥乎百家。腹中已具石渠宝藏。而蓄积既多。需用不穷。故其文也。纡馀赡博。不为深刻巉绝之论。而源深而流长。体肥而气完。无艰难辛苦之态。诗亦平实典雅。浏亮宛转。不沾沾于月露浮艳。而深得古人忠厚之味者。即君之本色然也。于乎。诵读知人。圣人有训。如使世之深知君者。为汝南之评。君之性质冲和。言为坦率。平生无一分计较屑琐底意。而熙熙天放。随遇而任其真。顾其弸中彪外。发而为文章者。虽欲强颜而作谄巧语。以取容于当世人眼目。必不可能。而亦非君之志也。彼不知者。妄以为侨窝之文。如列肆而府帑。无缄钥之固。诗有步趣而晚学依葫芦之画。此虽辈流间戏言。非出于思。而不过为撼树之蜉笑鹏之鴳而已。何足道哉。惜乎。以君才业之富。文章之盛。宜其受报收功。大有所展布于世者。而门瑟不工于齐。卞玉徒刖于楚。竟抹摋不得伸也。及其岁暮之日。往往短策玄马。徜徉山水间。遨游诗社中。朋酒为娱。以叙其碨磊不平之怀者。盖出于遗世自适意也。语曰达人知命。分。君子不怨尤。余于君。独何戚戚为哉。呜呼。天生吾辈。幸并一世。其穷不得志也同。其交而相随也久。有怀必达。有唱相和。今其一部所录。多是年来觞咏之迹也。君自为二小叙弁之。又要余置一言其间。余虽有小巫之㥘。其何说辞。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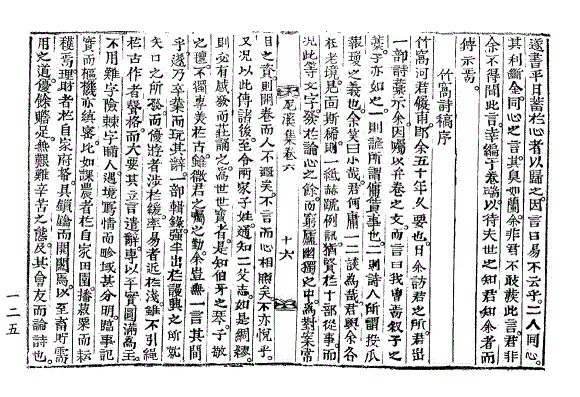 遂书平日蓄于心者以归之。因言曰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余非君不敢发此言。君非余不得闻此言。幸编于卷端。以待夫世之知君知余者而传示焉。
遂书平日蓄于心者以归之。因言曰易不云乎。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余非君不敢发此言。君非余不得闻此言。幸编于卷端。以待夫世之知君知余者而传示焉。竹窝诗稿序
竹窝河君履甫。即余五十年久要也。日余访君之所。君出一部诗藁示余。因嘱以弁卷之文。而言曰我曾焉叙子之藁。子亦如之。一则谚所谓佣赁事也。二则诗人所谓投瓜报琼之义也。余笑曰小哉。君何庸一二谈为哉。君与余各在老境。见面斯稀。则一纸赫𨂜例讯。犹贤于十部从事。而况此等文字。发于论心之馀。而穷庐幽独之中。为对案常目之资。则开卷而人不遐矣。不言而心相照矣。不亦悦乎。又况以此传诸后。至令两家子姓。通知二父志。如是绸缪。则必有感发而庄诵之。为世世宝者。是知伯牙之琴。子敬之毡。不独专美于古。虽微君之嘱之勤。余岂无一言其间乎。遂乃卒业而玩其辞。一部辑录。强半出于谩兴之所就。矢口之所发。而优游者涉于缓。率易者近于浅。虽不引绳于古作者声格。而大要其立言遣辞。专以平实圆满为主。不用难字险棘字瞒人。遇境写情而畛域甚分明。临事记实而枢机亦缜密。比如课农者于自家田园。播菽粟而耘穫焉。理财者于自家府帑。具锁钥而开阖焉。以至畜贮需用之道。优馀赡足。无艰难辛苦之态。及其会友而论诗也。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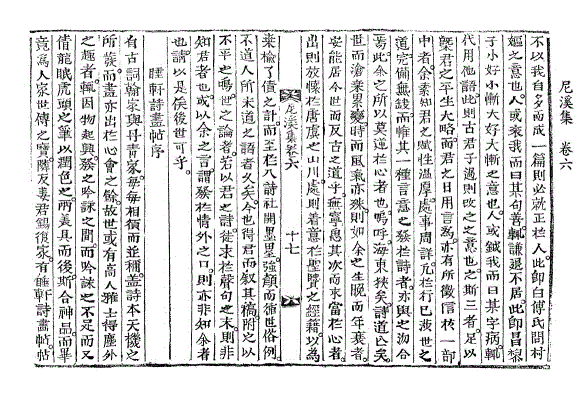 不以我自多而成一篇则必就正于人。此即白傅氏问村妪之意也。人或衮我而曰某句善。辄谦退不居。此即昌黎子小好小惭大好大惭之意也。人或钺我而曰某字病。辄代用他语。此则古君子过则改之之意也。之斯三者。足以槩君之平生大略。而君之日用言为。亦有所徵信于一部中者。余素知君之赋性温厚。处事周详。凡于行己涉世之道。完备无缺。而惟其一种言意之发于诗者。亦与之沕合焉。此余之所以莫逆于心者也。呜呼。海东狭矣。诗道亡矣。世而沧桑累变。时而风气亦殊。则如余之生晚而年衰者。安能居今世而反古之道乎。无宁思其次而求当于心者。出则放怀于唐虞之山川。处则着意于圣贤之经籍。以为桑榆了债之计。而至于入诗社开墨垒。强颜而循世俗例。不道人所未道之语者久矣。今也得君而叙其稿。附之以不平之鸣。世之论者。若以君之诗。徒求于声句之末。则非知君者也。或以余之言。谓发于情外之口。则亦非知余者也。请以是俟后世可乎。
不以我自多而成一篇则必就正于人。此即白傅氏问村妪之意也。人或衮我而曰某句善。辄谦退不居。此即昌黎子小好小惭大好大惭之意也。人或钺我而曰某字病。辄代用他语。此则古君子过则改之之意也。之斯三者。足以槩君之平生大略。而君之日用言为。亦有所徵信于一部中者。余素知君之赋性温厚。处事周详。凡于行己涉世之道。完备无缺。而惟其一种言意之发于诗者。亦与之沕合焉。此余之所以莫逆于心者也。呜呼。海东狭矣。诗道亡矣。世而沧桑累变。时而风气亦殊。则如余之生晚而年衰者。安能居今世而反古之道乎。无宁思其次而求当于心者。出则放怀于唐虞之山川。处则着意于圣贤之经籍。以为桑榆了债之计。而至于入诗社开墨垒。强颜而循世俗例。不道人所未道之语者久矣。今也得君而叙其稿。附之以不平之鸣。世之论者。若以君之诗。徒求于声句之末。则非知君者也。或以余之言。谓发于情外之口。则亦非知余者也。请以是俟后世可乎。睡轩诗画帖序
自古词翰家与丹青家。每每相须而并称。盖诗本天机之所发。而画亦出于心会之馀。故世或有高人雅士得尘外之趣者。辄因物起兴。发之吟咏之间。而吟咏之不足而又倩龙眠虎头之笔以润色之。两美具而后。斯合神品。而毕竟为人家世传之宝。邻友姜君锡复家。有睡轩诗画帖。帖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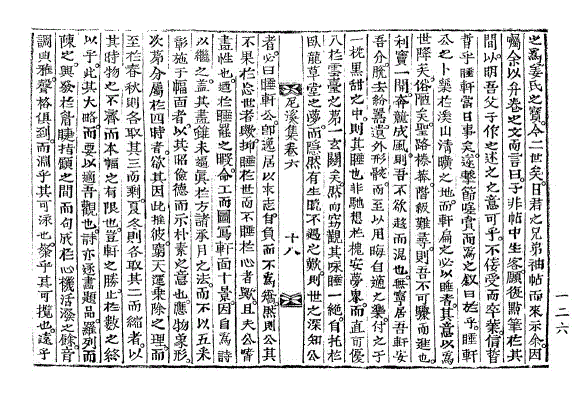 之为姜氏之宝。今二世矣。日君之兄弟袖帖而来示余。因嘱余以弁卷之文而言曰。子非帖中生客。愿复点笔于其间。以明吾父子作之述之之意可乎。不佞受而卒业。信晢晢乎睡轩当日事矣。遂击节嗟赏而为之叙曰于乎。睡轩公之卜筑于溪山清旷之地。而轩扁之必以睡者。其意以为世降矣。俗陋矣。圣路榛莽。阶级难寻。则吾不可骤而进也。利窦一开。奔竞成风。则吾不欲趍而混也。无宁居吾轩安吾分。脱去纷嚣。遗外形骸。而至以用晦自适之乐。付之于一枕黑甜之中。则其睡也非驰想于槐安梦界。而直可优入于云台之第一玄关矣。然而窃观其咏睡一绝。自托于卧龙草堂之梦。而隐然有生晚不遇之叹。则世之深知公者。必曰睡轩公。即逸居以求志。自负而不为矫。然则公其不果于忘世者欤。抑睡于世而不睡于心者欤。且夫公嗜画性也。乃于睡罢之暇。命工而图写轩面十景。因自为诗以继之。盖其画虽未逼真于方诸承月之法。而不以五采彰施于幅面者。以其昭俭德而示朴素之意也。应物象形。次第分属于四时者。欲其因此推彼。穷天运乘除之理。而至于春秋则各取其三而剩。夏冬则各取其二而缩者。以其时物之不齐而本幅之有限也。岂轩之胜。止于数之终以乎。此其大略。而要以适吾观也。诗亦逐画题品。罗列而陈之。兴发于眉睫指顾之间而句成于心机活泼之馀。音调典雅。声格俱到。而渊乎其可泳也。粲乎其可揽也。远乎
之为姜氏之宝。今二世矣。日君之兄弟袖帖而来示余。因嘱余以弁卷之文而言曰。子非帖中生客。愿复点笔于其间。以明吾父子作之述之之意可乎。不佞受而卒业。信晢晢乎睡轩当日事矣。遂击节嗟赏而为之叙曰于乎。睡轩公之卜筑于溪山清旷之地。而轩扁之必以睡者。其意以为世降矣。俗陋矣。圣路榛莽。阶级难寻。则吾不可骤而进也。利窦一开。奔竞成风。则吾不欲趍而混也。无宁居吾轩安吾分。脱去纷嚣。遗外形骸。而至以用晦自适之乐。付之于一枕黑甜之中。则其睡也非驰想于槐安梦界。而直可优入于云台之第一玄关矣。然而窃观其咏睡一绝。自托于卧龙草堂之梦。而隐然有生晚不遇之叹。则世之深知公者。必曰睡轩公。即逸居以求志。自负而不为矫。然则公其不果于忘世者欤。抑睡于世而不睡于心者欤。且夫公嗜画性也。乃于睡罢之暇。命工而图写轩面十景。因自为诗以继之。盖其画虽未逼真于方诸承月之法。而不以五采彰施于幅面者。以其昭俭德而示朴素之意也。应物象形。次第分属于四时者。欲其因此推彼。穷天运乘除之理。而至于春秋则各取其三而剩。夏冬则各取其二而缩者。以其时物之不齐而本幅之有限也。岂轩之胜。止于数之终以乎。此其大略。而要以适吾观也。诗亦逐画题品。罗列而陈之。兴发于眉睫指顾之间而句成于心机活泼之馀。音调典雅。声格俱到。而渊乎其可泳也。粲乎其可揽也。远乎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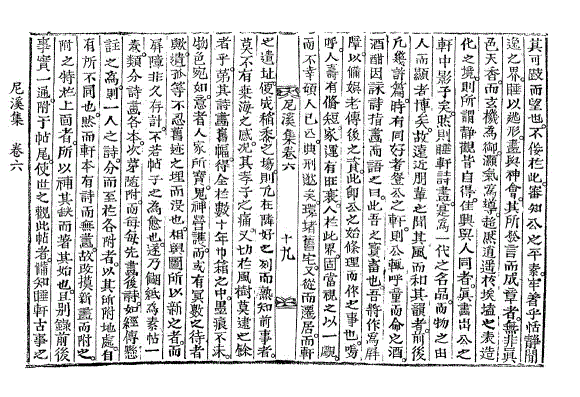 其可跂而望也。不佞于此。审知公之平素。牢着乎恬静閒逸之界。睡以逃形。画与神会。其所发言而成章者。无非真色天香。而玄机为御。灏气为导。超然逍遥于埃𡏖之表造化之境。则所谓静观皆自得。佳兴与人同者。真画出公之轩中影子矣。然则睡轩诗画。寔为一代之名品。而物之由人而显者博矣。故远近朋辈之闻其风而和其韵者。前后凡几许篇。时有同好者登公之轩。则公辄呼童而命之酒。酒酣因咏诗指画而语之曰。此吾之宝畜也。吾将作为屏障。以备娱老传后之资。此即公之始条理而作之事也。呜呼。人寿有脩短。家运有旺衰。人于此界。固当视之以一觑。而不幸硕人已亡。典刑逖矣。环堵旧宅。又从而迁居。而轩之遗址。便成稻黍之场。则凡在邻好之列而熟知前事者。莫不有桑海之感。况其孝子之痛。又切于风树莫逮之馀者乎。第其诗画旧幅。得全于数十年巾箱之中。墨痕不沫。物色宛如。意者人家所宝。鬼神营护。而或有冥数之待者欤。遗孤等不忍旧迹之埋而没也。相与图所以新之者。而屏障非久存计。不若帖子之为愈也。遂乃糊纸为素帖一卷。类分诗画各本。次第随附。而每每先画后诗。如经传悬注之为。则一人之诗。分而至于各附者。以其所附地处。自有所不同也。然而轩本有诗而无画。故改摸新画而附之。附之特于上面者。所以补其缺而著其始也。且别录前后事实一通。附于帖尾。使世之观此帖者。备知睡轩古事之
其可跂而望也。不佞于此。审知公之平素。牢着乎恬静閒逸之界。睡以逃形。画与神会。其所发言而成章者。无非真色天香。而玄机为御。灏气为导。超然逍遥于埃𡏖之表造化之境。则所谓静观皆自得。佳兴与人同者。真画出公之轩中影子矣。然则睡轩诗画。寔为一代之名品。而物之由人而显者博矣。故远近朋辈之闻其风而和其韵者。前后凡几许篇。时有同好者登公之轩。则公辄呼童而命之酒。酒酣因咏诗指画而语之曰。此吾之宝畜也。吾将作为屏障。以备娱老传后之资。此即公之始条理而作之事也。呜呼。人寿有脩短。家运有旺衰。人于此界。固当视之以一觑。而不幸硕人已亡。典刑逖矣。环堵旧宅。又从而迁居。而轩之遗址。便成稻黍之场。则凡在邻好之列而熟知前事者。莫不有桑海之感。况其孝子之痛。又切于风树莫逮之馀者乎。第其诗画旧幅。得全于数十年巾箱之中。墨痕不沫。物色宛如。意者人家所宝。鬼神营护。而或有冥数之待者欤。遗孤等不忍旧迹之埋而没也。相与图所以新之者。而屏障非久存计。不若帖子之为愈也。遂乃糊纸为素帖一卷。类分诗画各本。次第随附。而每每先画后诗。如经传悬注之为。则一人之诗。分而至于各附者。以其所附地处。自有所不同也。然而轩本有诗而无画。故改摸新画而附之。附之特于上面者。所以补其缺而著其始也。且别录前后事实一通。附于帖尾。使世之观此帖者。备知睡轩古事之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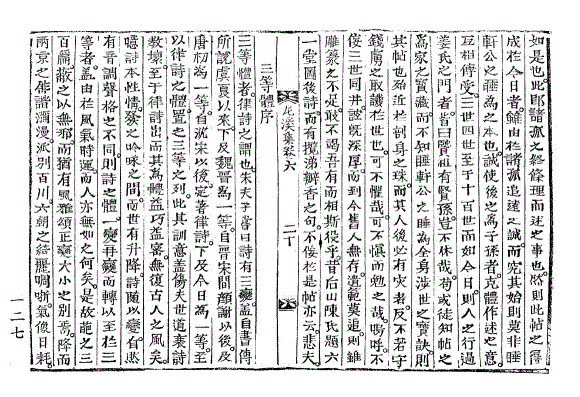 如是也。此即诸孤之终条理而述之事也。然则此帖之得成于今日者。虽由于诸孤追远之诚。而究其始则莫非睡轩公之睡为之本也。诚使后之为子孙者。克体作述之意。互相传受。三世四世至于十百世而如今日。则人之行过姜氏之门者。皆曰贤祖有贤孙。岂不休哉。苟或徒知帖之为家之宝藏。而不知睡轩公之睡为全身涉世之宝诀。则其帖也殆近于剖身之珠。而其人后必有灾者。反不若守钱虏之取讥于世也。可不惧哉。可不慎而勉之哉。呜呼。不佞三世同井。谊既深厚。而到今旧人无存。遗范莫追。则虽雕篆之不足。敢不竭吾有而相斯役乎。昔后山陈氏题六一堂图后诗。而有揽涕瓣香之句。不佞于是帖亦云。悲夫。
如是也。此即诸孤之终条理而述之事也。然则此帖之得成于今日者。虽由于诸孤追远之诚。而究其始则莫非睡轩公之睡为之本也。诚使后之为子孙者。克体作述之意。互相传受。三世四世至于十百世而如今日。则人之行过姜氏之门者。皆曰贤祖有贤孙。岂不休哉。苟或徒知帖之为家之宝藏。而不知睡轩公之睡为全身涉世之宝诀。则其帖也殆近于剖身之珠。而其人后必有灾者。反不若守钱虏之取讥于世也。可不惧哉。可不慎而勉之哉。呜呼。不佞三世同井。谊既深厚。而到今旧人无存。遗范莫追。则虽雕篆之不足。敢不竭吾有而相斯役乎。昔后山陈氏题六一堂图后诗。而有揽涕瓣香之句。不佞于是帖亦云。悲夫。三等体序
三等体者。律诗之谓也。朱夫子尝曰诗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说虞夏以来。下及魏晋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及唐初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为一等。至以律诗之体。置之三等之列。此其训意盖伤夫世道衰诗教坏。至于律诗出而其为体益巧益密。无复古人之风矣。噫诗本性情。发之吟咏之间。而世有升降。诗随以变。自然有音调声格之不同。则诗之体。一变再变而转以至于三等者。盖由于风气时运。而人亦无如之何矣。是故葩之三百篇。蔽之以无邪。而犹有风雅颂正变大小之别焉。降而两京之俳谐瀰漫。派别百川。六朝之绮丽啁哳。气像日耗。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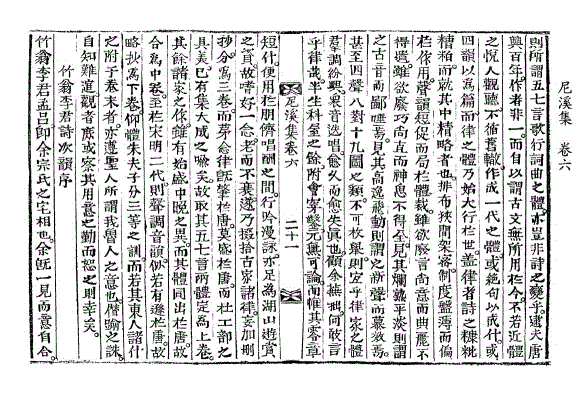 则所谓五七言歌行词曲之体。亦岂非诗之变乎。逮夫唐兴百年。作者非一。而自以谓古文无所用于今。不若近体之悦人观听。不循旧辙。作成一代之体。或绝句以成什。或四韵以为篇。而律之体乃始大行于世。盖律者诗之糠秕糟粕。而就其中精略者也。排布狭间架密。制度盘薄而偏于作用。声韵短促而局于体裁。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全。见其烂熟平淡则谓之古音而鄙唾焉。见其高逸飞动则谓之新声而慕效焉。甚至四声八对十九图之类。不可枚举。则宜乎律家之体群调纷兴。众音迭唱。愈久而愈失真也。顾余芜拙。何敢言乎律哉。半生科屋之馀。附会穿凿。元无可论。而惟其零章短什。便用于朋侪唱酬之间。行吟漫咏。亦足为湖山游赏之资。故嗜好一念。老而不衰。遂乃掇拾古家诸律。妄加删抄。分为三卷。而第念律既肇于唐。莫盛于唐。而杜工部之具美。已有集大成之喻矣。故取其五七言两体定为上卷。其馀诸家之作。虽有始盛中晚之异。而其体同出于唐。故合为中卷。至于宋明二代。则声调音韵。似若有逊于唐。故略抄为下卷。仰体朱夫子分三等之训。而若其东人诸什之附于卷末者。亦遵圣人所谓我鲁人之意也。僭踰之诛。自知难逭。观者庶或察其用意之勤而恕之则幸矣。
则所谓五七言歌行词曲之体。亦岂非诗之变乎。逮夫唐兴百年。作者非一。而自以谓古文无所用于今。不若近体之悦人观听。不循旧辙。作成一代之体。或绝句以成什。或四韵以为篇。而律之体乃始大行于世。盖律者诗之糠秕糟粕。而就其中精略者也。排布狭间架密。制度盘薄而偏于作用。声韵短促而局于体裁。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虽欲废巧尚直而神思不得全。见其烂熟平淡则谓之古音而鄙唾焉。见其高逸飞动则谓之新声而慕效焉。甚至四声八对十九图之类。不可枚举。则宜乎律家之体群调纷兴。众音迭唱。愈久而愈失真也。顾余芜拙。何敢言乎律哉。半生科屋之馀。附会穿凿。元无可论。而惟其零章短什。便用于朋侪唱酬之间。行吟漫咏。亦足为湖山游赏之资。故嗜好一念。老而不衰。遂乃掇拾古家诸律。妄加删抄。分为三卷。而第念律既肇于唐。莫盛于唐。而杜工部之具美。已有集大成之喻矣。故取其五七言两体定为上卷。其馀诸家之作。虽有始盛中晚之异。而其体同出于唐。故合为中卷。至于宋明二代。则声调音韵。似若有逊于唐。故略抄为下卷。仰体朱夫子分三等之训。而若其东人诸什之附于卷末者。亦遵圣人所谓我鲁人之意也。僭踰之诛。自知难逭。观者庶或察其用意之勤而恕之则幸矣。竹翁李君诗次韵序
竹翁李君孟吕。即余宗氏之宅相也。余既一见而意自合。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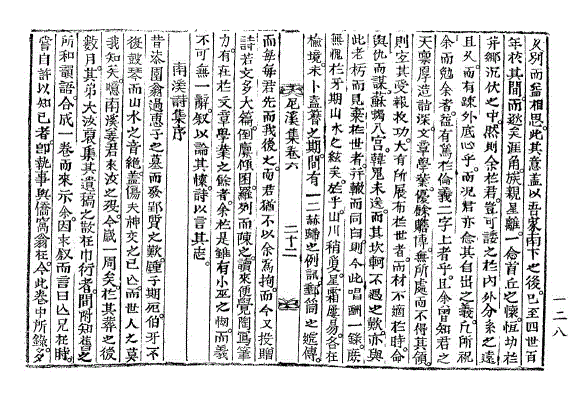 久别而益相思。此其意盖以吾家南下之后。已至四世百年于其间。而逖矣涯角。族亲星离。一念首丘之怀。恒切于并乡沉伏之中。然则余于君。岂可诿之于内外分系之远且久。而有疏外底心乎。而况君亦念其自出之义。凡所祝余而勉余者。益有笃于伦义二字上者乎。且余曾知君之天禀厚造诣深。文章学业。优馀赡博。无所处而不得其领。则宜其受报收功。大有所展布于世者。而材不适于时。命与仇而谋。苏蝎入宫。韩鬼未送。而其坎轲不遇之叹。亦与此老朽而见弃于世者。并辙而同臼。则今此唱酬一录。庶无愧于牙期山水之弦矣。于乎。山川稍夐。星霜屡易。各在榆境。未卜盍簪之期。间有一二赫蹄之例讯。邮筒之递传。而每每君先而我后之。而君犹不以余为拘。而今又投赠诗若文多大篇。倒廪倾囷。罗列而陈之。读来便觉陶写笔力。有在于文章学业之馀者。余于是虽有小巫之㥘。而义不可无一辞。叙以论其怀。诗以言其志。
久别而益相思。此其意盖以吾家南下之后。已至四世百年于其间。而逖矣涯角。族亲星离。一念首丘之怀。恒切于并乡沉伏之中。然则余于君。岂可诿之于内外分系之远且久。而有疏外底心乎。而况君亦念其自出之义。凡所祝余而勉余者。益有笃于伦义二字上者乎。且余曾知君之天禀厚造诣深。文章学业。优馀赡博。无所处而不得其领。则宜其受报收功。大有所展布于世者。而材不适于时。命与仇而谋。苏蝎入宫。韩鬼未送。而其坎轲不遇之叹。亦与此老朽而见弃于世者。并辙而同臼。则今此唱酬一录。庶无愧于牙期山水之弦矣。于乎。山川稍夐。星霜屡易。各在榆境。未卜盍簪之期。间有一二赫蹄之例讯。邮筒之递传。而每每君先而我后之。而君犹不以余为拘。而今又投赠诗若文多大篇。倒廪倾囷。罗列而陈之。读来便觉陶写笔力。有在于文章学业之馀者。余于是虽有小巫之㥘。而义不可无一辞。叙以论其怀。诗以言其志。南溪诗集序
昔㓒园翁过惠子之墓而发郢质之叹。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而山水之音绝。盖伤夫神交之已亡。而世人之莫我知矣。噫南溪姜君来汝之殁。今岁一周矣。于其葬之后数月。其弟大汝裒集其遗稿之散在巾衍者。间附知旧之所和韵语。合成一卷而来示余。因求叙而言曰亡兄在时。尝自许以知己者。即执事与侨窝翁在。今此卷中所录。多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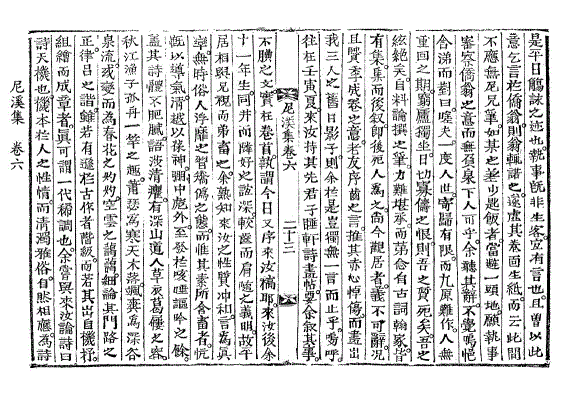 是平日觞咏之迹也。执事既非生客。宜有言也。且曾以此意乞言于侨翁。则翁辄诺之。遂虚其卷面生纸。而云此间不应无尼兄笔。如某之差少匙饭者。当避一头地。愿执事审察侨翁之意而无负泉下人可乎。余听其辞。不觉呜悒含涕而对曰。嗟夫。一度人世。寄归有限。而九原难作。人无重回之期。穷庐独坐。日切寡俦之恨。则吾之质死矣。吾之弦绝矣。自料论撰之笔。力难堪承。而第念自古词翰家。皆有集。集而后叙。即后死人为之。尚今观居者。义不可辞。况且贤季成卷之意。老友序齿之言。推其赤心悼伤。而画出我三人之旧日影子。则余于是岂独无一言而止乎。呜呼。往在壬寅夏。来汝持其先君子睡轩诗画帖。要余叙其事。不腆之文。实在卷首。孰谓今日又序来汝稿耶。来汝后余十一年生。同井而邻好之谊深。较齿而肩随之义明。故平居相与兄视而弟畜之。余熟知来汝之性质冲和。言为真率。无时俗人浮靡之习矫伪之态。而惟其素所含畜者。忼慨以导气。清越以葆神。弸中彪外。至发于咳唾讴吟之馀。盖其诗体不肥腻。语涉清癯。有深山道人草衣葛屦之容。秋江渔子孤舟一竿之趣。萧瑟为寒天木落。飒爽为深谷泉流。或变而为春花之灼灼。空云之蔼蔼。细论其门路之正。律吕之谐。虽若有逊于古作者阶级。而若其出自机抒。组绘而成章者。真可谓一代稀调也。余尝与来汝论诗曰诗天机也。机本于人之性情。而清浊雅俗。自然相应。为诗
是平日觞咏之迹也。执事既非生客。宜有言也。且曾以此意乞言于侨翁。则翁辄诺之。遂虚其卷面生纸。而云此间不应无尼兄笔。如某之差少匙饭者。当避一头地。愿执事审察侨翁之意而无负泉下人可乎。余听其辞。不觉呜悒含涕而对曰。嗟夫。一度人世。寄归有限。而九原难作。人无重回之期。穷庐独坐。日切寡俦之恨。则吾之质死矣。吾之弦绝矣。自料论撰之笔。力难堪承。而第念自古词翰家。皆有集。集而后叙。即后死人为之。尚今观居者。义不可辞。况且贤季成卷之意。老友序齿之言。推其赤心悼伤。而画出我三人之旧日影子。则余于是岂独无一言而止乎。呜呼。往在壬寅夏。来汝持其先君子睡轩诗画帖。要余叙其事。不腆之文。实在卷首。孰谓今日又序来汝稿耶。来汝后余十一年生。同井而邻好之谊深。较齿而肩随之义明。故平居相与兄视而弟畜之。余熟知来汝之性质冲和。言为真率。无时俗人浮靡之习矫伪之态。而惟其素所含畜者。忼慨以导气。清越以葆神。弸中彪外。至发于咳唾讴吟之馀。盖其诗体不肥腻。语涉清癯。有深山道人草衣葛屦之容。秋江渔子孤舟一竿之趣。萧瑟为寒天木落。飒爽为深谷泉流。或变而为春花之灼灼。空云之蔼蔼。细论其门路之正。律吕之谐。虽若有逊于古作者阶级。而若其出自机抒。组绘而成章者。真可谓一代稀调也。余尝与来汝论诗曰诗天机也。机本于人之性情。而清浊雅俗。自然相应。为诗尼溪集卷之六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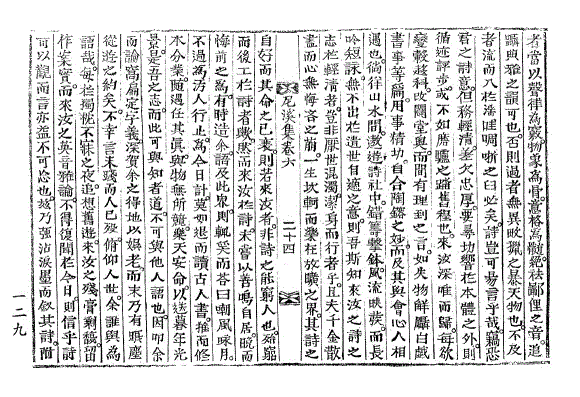 者当以声律为窍。物象为骨。意格为髓。绝祛鄙俚之音。追蹑典雅之韵可也。否则过者无异畋猎之暴天物也。不及者流而入于淫哇啁哳之臼必矣。诗岂可易言乎哉。窃恐君之诗意。但务轻清。差欠忠厚。要寻切响于本体之外。则循迹评步。或不如磨驴之踏旧程也。来汝深唯而归。每欲变毂趍科。改辟堂奥。而间有理到之言。如失物解镊白戏书事等篇。用事精切。自合陶镕之妙。而及其与会心人相遇也。徜徉山水间。遨游诗社中。错筹击钵。风流映发。而长吟短咏。无不出于遗世自适之意。则吾斯知来汝之诗之志于轻清者。岂非厌世混浊。洁身而行者乎。且夫千金散尽而心无悔吝之萌。一生坎轲而乐在放旷之界。其诗之自好而其命之已衰。则若来汝者。非诗之能穷人也。殆穷而后工于诗者欤。然而来汝于诗。未尝以善鸣自居。晚而悔前之为。有时造余。语及此界。则辄笑而答曰嘲风咏月。不过为污人行止。为今日计。莫如退而读古人书。推而修本分业。随遇任其真。与物无所竞。乐天安命。以送暮年光景。是吾之志。而此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他人语也。因叩余而论窝扁定字义。深贺余之得地以娱老。而末乃有蹑尘从游之约矣。不幸言未践而人已殁。俯仰人世。余谁与为语哉。每于独枕不寐之夜。追想旧游。来汝之残膏剩馥。留作案实。而来汝之英音雅论。不得复闻于今日。则信乎诗可以观而言亦益不可忘也。玆乃强沾泪墨而叙其诗。附
者当以声律为窍。物象为骨。意格为髓。绝祛鄙俚之音。追蹑典雅之韵可也。否则过者无异畋猎之暴天物也。不及者流而入于淫哇啁哳之臼必矣。诗岂可易言乎哉。窃恐君之诗意。但务轻清。差欠忠厚。要寻切响于本体之外。则循迹评步。或不如磨驴之踏旧程也。来汝深唯而归。每欲变毂趍科。改辟堂奥。而间有理到之言。如失物解镊白戏书事等篇。用事精切。自合陶镕之妙。而及其与会心人相遇也。徜徉山水间。遨游诗社中。错筹击钵。风流映发。而长吟短咏。无不出于遗世自适之意。则吾斯知来汝之诗之志于轻清者。岂非厌世混浊。洁身而行者乎。且夫千金散尽而心无悔吝之萌。一生坎轲而乐在放旷之界。其诗之自好而其命之已衰。则若来汝者。非诗之能穷人也。殆穷而后工于诗者欤。然而来汝于诗。未尝以善鸣自居。晚而悔前之为。有时造余。语及此界。则辄笑而答曰嘲风咏月。不过为污人行止。为今日计。莫如退而读古人书。推而修本分业。随遇任其真。与物无所竞。乐天安命。以送暮年光景。是吾之志。而此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他人语也。因叩余而论窝扁定字义。深贺余之得地以娱老。而末乃有蹑尘从游之约矣。不幸言未践而人已殁。俯仰人世。余谁与为语哉。每于独枕不寐之夜。追想旧游。来汝之残膏剩馥。留作案实。而来汝之英音雅论。不得复闻于今日。则信乎诗可以观而言亦益不可忘也。玆乃强沾泪墨而叙其诗。附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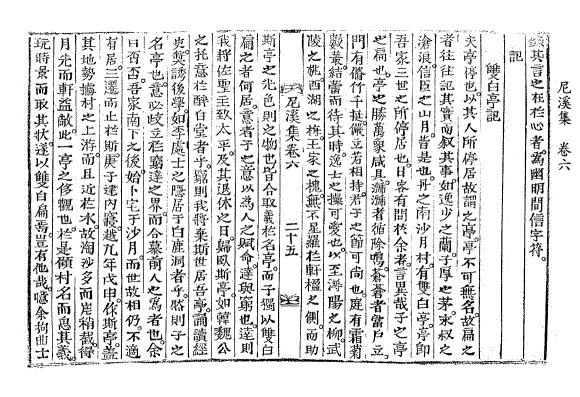 录其言之在于心者。为幽明间信字符。
录其言之在于心者。为幽明间信字符。尼溪集卷之六
记
双白亭记
夫亭停也。以其人所停居故谓之亭。亭不可无名。故扁之者往往记其实而叙其事。如逸少之兰。子厚之茅。永叔之沧浪。信臣之山月。皆是也。丹之南沙月村。有双白亭。亭即吾家三世之所停居也。日客有问于余者。言异哉子之亭之扁也。亭之胜万象咸具。㶁㶁者循除鸣。苍苍者当户立。门有脩竹千挺。俨立若相持。君子之节可尚也。庭有霜菊数丛。结蕾而待其时。逸士之操可爱也。以至浔阳之柳。武陵之桃。西湖之梅。王家之槐。无不星罗于轩楹之侧。而助斯亭之光色则之物也皆合取义于名亭。而子独以双白扁之者何居。意者子之意以为人之赋命。达与穷也。达则我将佐圣主致太平。及其退休之日。归卧斯亭。如韩魏公之托意于醉白堂者乎。穷则我将弃斯世居吾亭。诵读经史。奖诱后学。如李处士之隐居于白鹿洞者乎。然则子之名亭也。意必歧立于穷达之界。而合慕前人之为者也。余曰否否。吾家南下之后。始卜宅于沙月。而世故相仍。不适有居。三迁而止于斯。庚子建内寝。越九年戊申。作斯亭。盖其地势据村之上游。而且近于水。故淘沙多而岸稍截。得月先而轩益敞。此一亭之侈观也。于是顾村名而思其义。玩时景而取其状。遂以双白扁焉。岂有他哉。噫余拘曲士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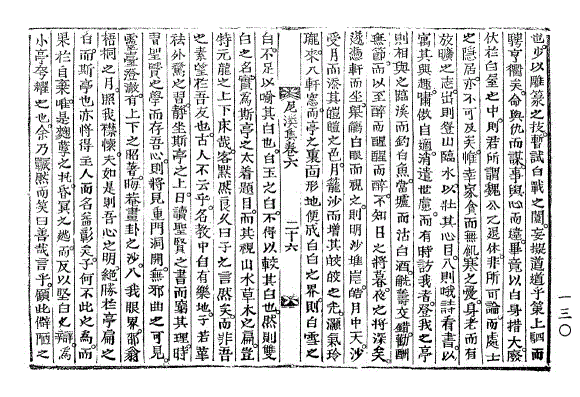 也。少以雕篆之技。暂试白战之闱。妄拟遒遒乎策上驷而骋亨衢矣。命与仇而谋。事与心而违。毕竟以白身措大。废伏于白屋之中。则君所谓魏公之退休。非所可论。而处士之隐居。亦不可及矣。惟幸家贫而无饥寒之忧。身老而有放旷之志。出则登山临水。以壮其心目。入则哦诗看书。以寓其兴趣。啸傲自适。消遣世虑。而有时访我者。登我之亭则相与之临溪而钓白鱼。当垆而沽白酒。觥筹交错。劝酬无节。而以至醉而醒醒而醉。不知日之将暮。夜之将深矣。遂凭轩而坐。举觞白眼而视之。则明沙堆岸。皓月中天。沙受月而添其皑皑之色。月笼沙而增其皎皎之光。灏气玲珑。来入轩窗。而亭之里面形地便成白白之界。则白雪之白。不足以喻其白也。白玉之白。不得以较其白也。然则双白之名。实为斯亭之太着题目。而其视山水草木之扁。岂特元龙之上下床哉。客默然良久曰子之言然矣。而非吾之素望于吾友也。古人不云乎。名教中自有乐地。子若革祛外骛之习。静坐斯亭之上。日读圣贤之书而穷其理。时习圣贤之学而存吾心。则将见重门洞开。无邪曲之可见。灵台澄澈。有上下之昭著。晦庵画卦之沙。入我眼界。邵翁梧桐之月。照我襟怀。夫如是则吾心之明。绝胜于亭扁之白。而斯亭也亦将得主人而名益彰矣。子何不此之为。而果于自弃。唯是曲孽之托。昏冥之逃。而反以坚白之辩。为小亭夸耀之也。余乃辴然而笑曰善哉言乎。顾此僻陋之
也。少以雕篆之技。暂试白战之闱。妄拟遒遒乎策上驷而骋亨衢矣。命与仇而谋。事与心而违。毕竟以白身措大。废伏于白屋之中。则君所谓魏公之退休。非所可论。而处士之隐居。亦不可及矣。惟幸家贫而无饥寒之忧。身老而有放旷之志。出则登山临水。以壮其心目。入则哦诗看书。以寓其兴趣。啸傲自适。消遣世虑。而有时访我者。登我之亭则相与之临溪而钓白鱼。当垆而沽白酒。觥筹交错。劝酬无节。而以至醉而醒醒而醉。不知日之将暮。夜之将深矣。遂凭轩而坐。举觞白眼而视之。则明沙堆岸。皓月中天。沙受月而添其皑皑之色。月笼沙而增其皎皎之光。灏气玲珑。来入轩窗。而亭之里面形地便成白白之界。则白雪之白。不足以喻其白也。白玉之白。不得以较其白也。然则双白之名。实为斯亭之太着题目。而其视山水草木之扁。岂特元龙之上下床哉。客默然良久曰子之言然矣。而非吾之素望于吾友也。古人不云乎。名教中自有乐地。子若革祛外骛之习。静坐斯亭之上。日读圣贤之书而穷其理。时习圣贤之学而存吾心。则将见重门洞开。无邪曲之可见。灵台澄澈。有上下之昭著。晦庵画卦之沙。入我眼界。邵翁梧桐之月。照我襟怀。夫如是则吾心之明。绝胜于亭扁之白。而斯亭也亦将得主人而名益彰矣。子何不此之为。而果于自弃。唯是曲孽之托。昏冥之逃。而反以坚白之辩。为小亭夸耀之也。余乃辴然而笑曰善哉言乎。顾此僻陋之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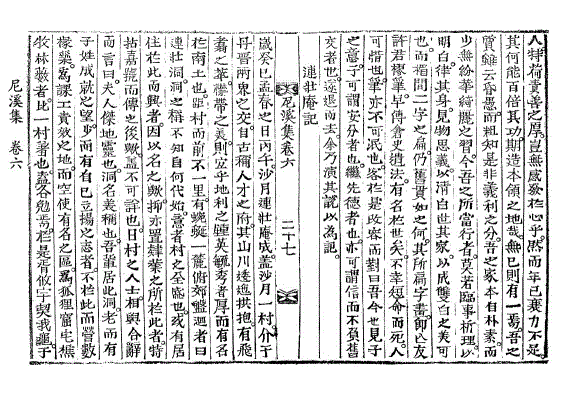 人。特荷责善之厚。岂无感发于心乎。然而年已衰力不足。其何能百倍其功。期造本领之地哉。无已则有一焉。吾之质虽云昏愚。而粗知是非义利之分。吾之家本自朴素。而少无纷华绮丽之习。今吾之所当行者。莫若临事析理。以明白。律其身。见物思义。以清白世其家。以成双白之美可也。而楣间二字之扁。仍旧贯如之何。其所扁字画。即亡友许君樛笔。早传仓史遗法。有名于世矣。不幸短命而死。人可惜也。笔亦不可泯也。客于是改容而对曰吾今也见子之意。子可谓安分者也。继先德者也。亦可谓信而不负旧交者也。遂退而去。余乃演其说以为记。
人。特荷责善之厚。岂无感发于心乎。然而年已衰力不足。其何能百倍其功。期造本领之地哉。无已则有一焉。吾之质虽云昏愚。而粗知是非义利之分。吾之家本自朴素。而少无纷华绮丽之习。今吾之所当行者。莫若临事析理。以明白。律其身。见物思义。以清白世其家。以成双白之美可也。而楣间二字之扁。仍旧贯如之何。其所扁字画。即亡友许君樛笔。早传仓史遗法。有名于世矣。不幸短命而死。人可惜也。笔亦不可泯也。客于是改容而对曰吾今也见子之意。子可谓安分者也。继先德者也。亦可谓信而不负旧交者也。遂退而去。余乃演其说以为记。连壮庵记
岁癸巳孟春之日丙午。沙月连壮庵成。盖沙月一村。介于丹晋两界之交。自古称人才之府。其山川逶迤拱抱。有飞翥之萃。襟带之美。则宜乎地利之钟英毓秀者厚而有名于南土也。距村而前不一里。有蜿蜒一麓俯郊盘回者曰连壮洞。洞之称不知自何代始。意者村之全盛也。或有居住于此而兴者。因以名之欤。抑亦置肄业之所于此者。特拈嘉号而传之后欤。盖不可详也。日村之人士。相与合辞而言曰。夫人杰地灵也。洞名美称也。吾辈居此洞。老而有子姓成就之望。少而有自己立扬之志者。不于此而营数椽筑。为课工责效之地。而空使有名之区。为狐狸窟宅樵牧林薮者。比一村羞也。盍各勉焉。于是胥攸宇契我龟。于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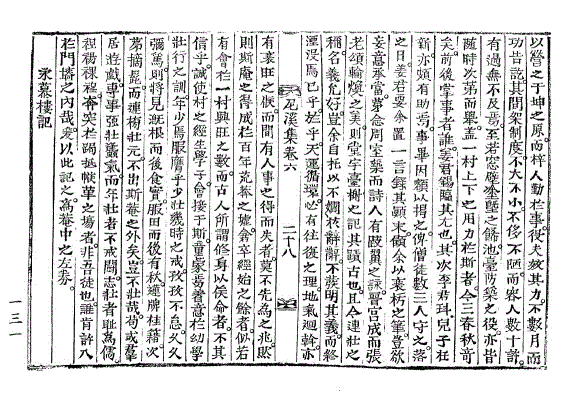 以营之于坤之原。而梓人勤于事。役夫效其力。不数月而功告讫。其间架制度。不大不小。不侈不陋。而容人数十许。有过无不及焉。至若窗壁涂塈之饰。池台防筑之役。亦皆随时次第而举。盖一村上下之用力于斯者。今三春秋奇矣。前后掌事者谁。姜君锡临其尤也。其次李君㺶,儿子在新。亦颇有助焉。事毕因额以揭之。俾僧徒数三人守之。落之日。姜君要余置一言录其颠末。顾余以衰朽之笔。岂欲妄意承当。第念周室筑而诗人有跂翼之咏。晋宫成而张老颂轮焕之美。则堂宇台榭之记其迹古也。且今连壮之称。名义允好。岂余自托以不娴于辞辞。不发明其义。而终湮没焉已乎。于乎。天运循环。必有往复之理。地气回斡。亦有衰旺之候。而间有人事之得而失者。莫不先为之兆。然则斯庵之得成于百年荒莽之墟。仓卒经始之馀者。似若有会于一村兴旺之数。而古人所谓修身以俟命者。不其信乎。诚使村之经生学子。会接于斯。童蒙焉着意于幼学壮行之训。年少焉服膺乎少壮几时之戒。孜孜不怠。久久弥笃。则将见溉根而后食实。服田而后有秋。莲牌桂籍。次第摘髭。而连榜壮元。不出斯庵之外矣。岂不壮哉。苟或群居游戏。专事强壮蜂气。而年壮者不戒斗。志壮者耻为儒。袒裼裸裎。奔突于跼抵帿革之场者。非吾徒也。谁肯许入于门墙之内哉。爰以此记之。为庵中之左券。
以营之于坤之原。而梓人勤于事。役夫效其力。不数月而功告讫。其间架制度。不大不小。不侈不陋。而容人数十许。有过无不及焉。至若窗壁涂塈之饰。池台防筑之役。亦皆随时次第而举。盖一村上下之用力于斯者。今三春秋奇矣。前后掌事者谁。姜君锡临其尤也。其次李君㺶,儿子在新。亦颇有助焉。事毕因额以揭之。俾僧徒数三人守之。落之日。姜君要余置一言录其颠末。顾余以衰朽之笔。岂欲妄意承当。第念周室筑而诗人有跂翼之咏。晋宫成而张老颂轮焕之美。则堂宇台榭之记其迹古也。且今连壮之称。名义允好。岂余自托以不娴于辞辞。不发明其义。而终湮没焉已乎。于乎。天运循环。必有往复之理。地气回斡。亦有衰旺之候。而间有人事之得而失者。莫不先为之兆。然则斯庵之得成于百年荒莽之墟。仓卒经始之馀者。似若有会于一村兴旺之数。而古人所谓修身以俟命者。不其信乎。诚使村之经生学子。会接于斯。童蒙焉着意于幼学壮行之训。年少焉服膺乎少壮几时之戒。孜孜不怠。久久弥笃。则将见溉根而后食实。服田而后有秋。莲牌桂籍。次第摘髭。而连榜壮元。不出斯庵之外矣。岂不壮哉。苟或群居游戏。专事强壮蜂气。而年壮者不戒斗。志壮者耻为儒。袒裼裸裎。奔突于跼抵帿革之场者。非吾徒也。谁肯许入于门墙之内哉。爰以此记之。为庵中之左券。永慕楼记
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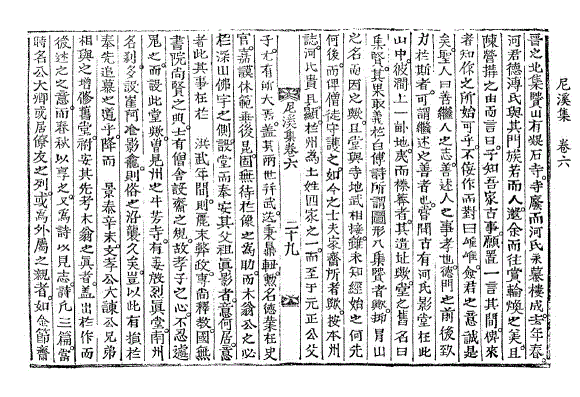 晋之北集贤山有凝石寺。寺废而河氏永慕楼成。去年春。河君德溥氏与其门族若而人。邀余而往赏轮焕之美。且陈营搆之由而言曰。子知吾家古事。愿置一言其间。俾来者知作之所始可乎。不佞作而对曰唯唯。佥君之意诚是矣。圣人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孝也。德门之前后致力于斯者。可谓继述之善者也。尝闻古有河氏影堂在此山中。彼涧上一亩地。夷而榛莽者。其遗址欤。堂之旧名曰集贤。其果取义于白傅诗所谓图形入集贤者欤。抑冒山之名而因之欤。且堂与寺地武相接。虽未知经始之何先何后。而俾僧徒守护之。如今之士夫家斋所者欤。按本州志。河氏贵具显。于州为土姓四家之一。而至于元正公父子。尤有所大焉。盖其两世并武。迭秉鼎轴。勋名德业在史官。嘉谟休范垂后昆。固无待于像之为助。而木翁公之必于深山佛宇之侧。设堂而奉安其父祖真影者。意何居。意者此其事在于 洪武年间。则丽末㢢政。专尚释教。国无书院尚贤之典。士有僧舍设斋之规。故孝子之心。不忍遽鬼之。而设此堂欤。曾见州之牛芳寺。有姜殷烈真堂。南州名刹。多设崔阿餐影龛。则俗之沿袭久矣。岂以此有损于奉先追慕之道乎。降而 景泰辛未。文孝公大谏公兄弟相与之增修旧堂。祔安其先考木翁之真者。盖出于作而后述之之意。而春秋以享之。又为诗以见志。诗凡三篇。当时名公大卿或居僚友之列。或为外属之亲者。如金节斋
晋之北集贤山有凝石寺。寺废而河氏永慕楼成。去年春。河君德溥氏与其门族若而人。邀余而往赏轮焕之美。且陈营搆之由而言曰。子知吾家古事。愿置一言其间。俾来者知作之所始可乎。不佞作而对曰唯唯。佥君之意诚是矣。圣人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孝也。德门之前后致力于斯者。可谓继述之善者也。尝闻古有河氏影堂在此山中。彼涧上一亩地。夷而榛莽者。其遗址欤。堂之旧名曰集贤。其果取义于白傅诗所谓图形入集贤者欤。抑冒山之名而因之欤。且堂与寺地武相接。虽未知经始之何先何后。而俾僧徒守护之。如今之士夫家斋所者欤。按本州志。河氏贵具显。于州为土姓四家之一。而至于元正公父子。尤有所大焉。盖其两世并武。迭秉鼎轴。勋名德业在史官。嘉谟休范垂后昆。固无待于像之为助。而木翁公之必于深山佛宇之侧。设堂而奉安其父祖真影者。意何居。意者此其事在于 洪武年间。则丽末㢢政。专尚释教。国无书院尚贤之典。士有僧舍设斋之规。故孝子之心。不忍遽鬼之。而设此堂欤。曾见州之牛芳寺。有姜殷烈真堂。南州名刹。多设崔阿餐影龛。则俗之沿袭久矣。岂以此有损于奉先追慕之道乎。降而 景泰辛未。文孝公大谏公兄弟相与之增修旧堂。祔安其先考木翁之真者。盖出于作而后述之之意。而春秋以享之。又为诗以见志。诗凡三篇。当时名公大卿或居僚友之列。或为外属之亲者。如金节斋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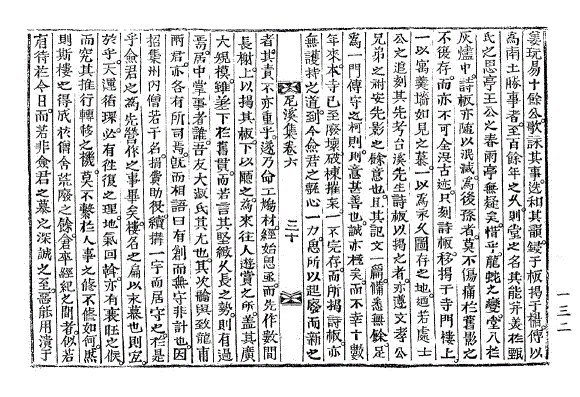 姜玩易十馀公。歌咏其事。迭和其韵。锓于板揭于楣。传以为南土胜事者。至百馀年之久。则堂之名其能并美于甄氏之思亭王公之春雨亭无疑矣。惜乎。龙蛇之变。堂入于灰烬中。诗板亦随以泯灭。为后孙者。莫不伤痛于旧影之不复存。而亦不可全没古迹。只刻诗板。移揭于寺门楼上。一以寓羹墙如见之慕。一以为永久图存之地。乃若处士公之追刻其先考台溪先生诗板以揭之者。亦遵文孝公兄弟之祔安先影之馀意也。且其记文一篇。备悉无馀。足为一门传守之柯则。则意甚善也。诚亦极矣。而不幸十数年来。本寺已至废坏。破栋摧杗。一不完存。而所揭诗板。亦无护持之道。到今佥君之砖心一力。思所以起废而新之者。其责不亦重乎。遂乃命工鸠材。经始思亟。而先作数间长榭。上以揭其板。下以厅之。为来往人游赏之所。盖其广大规模。虽差下于旧贯。而若言其坚致久长之势。则有过焉。居中掌事者谁。吾友大淑氏其尤也。其次𦪙与致龙甫两君。亦各有所司焉。既而相语曰有创而无守非计也。因招集州内僧若干名。捐费助役。续搆一宇而居守之。于是乎佥君之为先营作之事毕矣。楼名之扁以永慕也则宜。于乎。天运循环。必有往复之理。地气回斡。亦有衰旺之候。而究其推行转移之机。莫不系于人事之修不修如何。然则斯楼之得成于僧舍荒废之馀。仓卒经纪之间者。似若有待于今日。而若非佥君之慕之深诚之至。恶能用溃于
姜玩易十馀公。歌咏其事。迭和其韵。锓于板揭于楣。传以为南土胜事者。至百馀年之久。则堂之名其能并美于甄氏之思亭王公之春雨亭无疑矣。惜乎。龙蛇之变。堂入于灰烬中。诗板亦随以泯灭。为后孙者。莫不伤痛于旧影之不复存。而亦不可全没古迹。只刻诗板。移揭于寺门楼上。一以寓羹墙如见之慕。一以为永久图存之地。乃若处士公之追刻其先考台溪先生诗板以揭之者。亦遵文孝公兄弟之祔安先影之馀意也。且其记文一篇。备悉无馀。足为一门传守之柯则。则意甚善也。诚亦极矣。而不幸十数年来。本寺已至废坏。破栋摧杗。一不完存。而所揭诗板。亦无护持之道。到今佥君之砖心一力。思所以起废而新之者。其责不亦重乎。遂乃命工鸠材。经始思亟。而先作数间长榭。上以揭其板。下以厅之。为来往人游赏之所。盖其广大规模。虽差下于旧贯。而若言其坚致久长之势。则有过焉。居中掌事者谁。吾友大淑氏其尤也。其次𦪙与致龙甫两君。亦各有所司焉。既而相语曰有创而无守非计也。因招集州内僧若干名。捐费助役。续搆一宇而居守之。于是乎佥君之为先营作之事毕矣。楼名之扁以永慕也则宜。于乎。天运循环。必有往复之理。地气回斡。亦有衰旺之候。而究其推行转移之机。莫不系于人事之修不修如何。然则斯楼之得成于僧舍荒废之馀。仓卒经纪之间者。似若有待于今日。而若非佥君之慕之深诚之至。恶能用溃于尼溪集卷之六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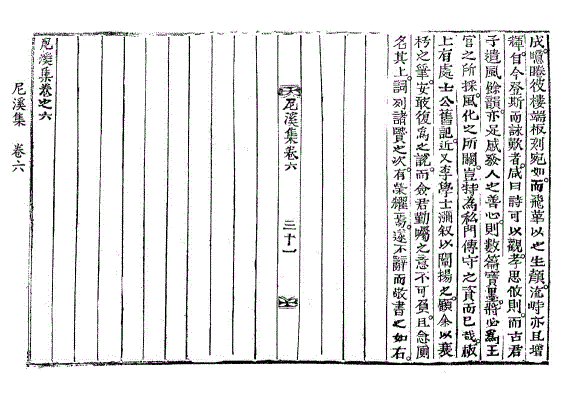 成。噫眷彼楼端板刻宛如。而飞革以之生颜。流峙亦且增辉。自今登斯而咏叹者。咸曰诗可以观。孝思攸则。而古君子遗风馀韵。亦足感发人之善心。则数篇宝墨。将必为王官之所采。风化之所关。岂特为私门传守之资而已哉。板上有处士公旧记。近又李学士瀰叙以阐扬之。顾余以衰朽之笔。安敢复为之说。而佥君勤嘱之意不可负。且念厕名其上。词列诸贤之次。有荣耀焉。遂不辞而敬书之如右。
成。噫眷彼楼端板刻宛如。而飞革以之生颜。流峙亦且增辉。自今登斯而咏叹者。咸曰诗可以观。孝思攸则。而古君子遗风馀韵。亦足感发人之善心。则数篇宝墨。将必为王官之所采。风化之所关。岂特为私门传守之资而已哉。板上有处士公旧记。近又李学士瀰叙以阐扬之。顾余以衰朽之笔。安敢复为之说。而佥君勤嘱之意不可负。且念厕名其上。词列诸贤之次。有荣耀焉。遂不辞而敬书之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