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0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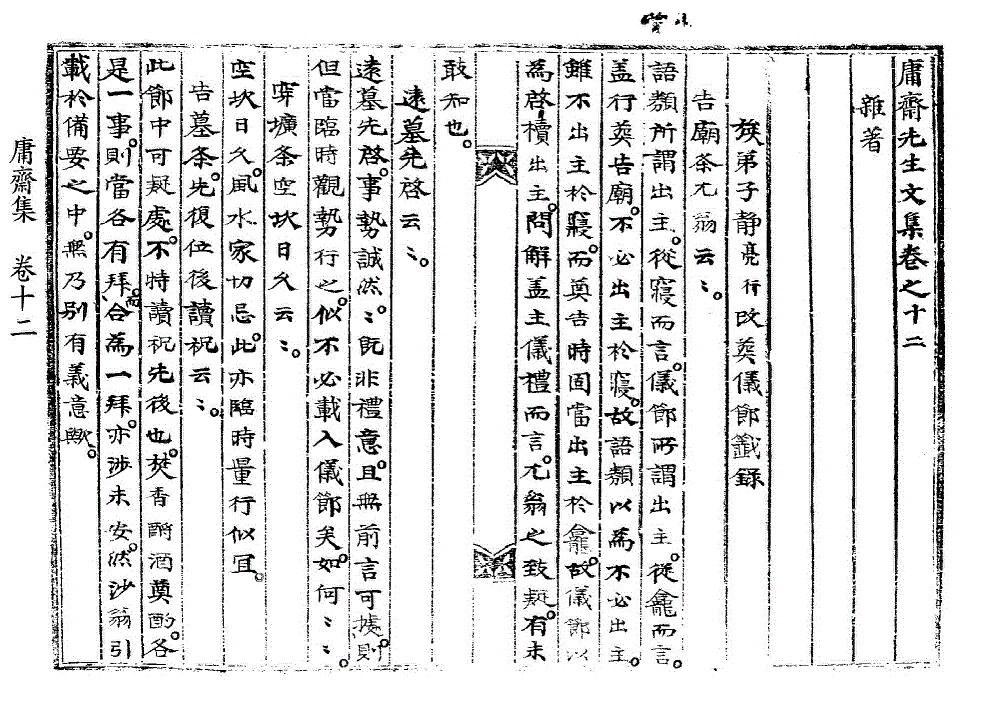 族弟子静(亮行)改葬仪节签录
族弟子静(亮行)改葬仪节签录告庙条尤翁云云。
语类所谓出主。从寝而言。仪节所谓出主。从龛而言。盖行葬告庙。不必出主于寝。故语类以为不必出主。虽不出主于寝。而奠告时固当出主于龛。故仪节以为启椟出主。问解盖主仪礼而言。尤翁之致疑。有未敢知也。
远墓先启云云。
远墓先启。事势诚然。然既非礼意。且无前言可据。则但当临时观势行之。似不必载入仪节矣。如何如何。
穿圹条空坎日久云云。
空坎日久。风水家切忌。此亦临时量行似宜。
告墓条。先复位后读祝云云。
此节中可疑处。不特读祝先后也。焚香酹酒奠酌。各是一事。则当各有拜。而合为一拜。亦涉未安。然沙翁引载于备要之中。无乃别有义意欤。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0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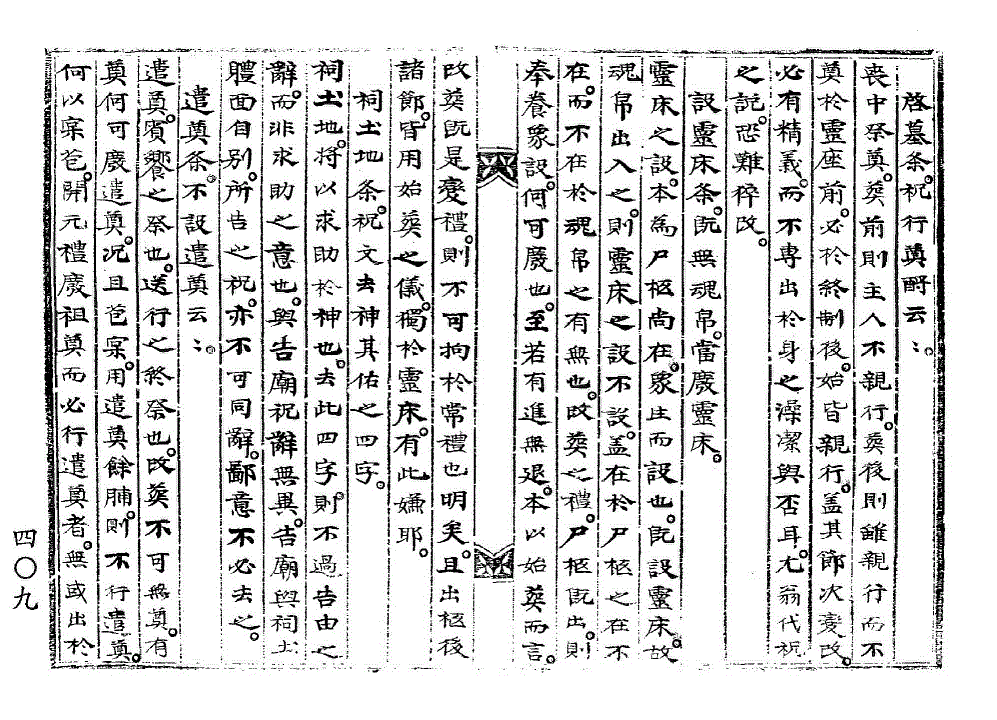 启墓条。祝行奠酹云云。
启墓条。祝行奠酹云云。丧中祭奠。葬前则主人不亲行。葬后则虽亲行而不奠于灵座前。必于终制后。始皆亲行。盖其节次变改。必有精义。而不专出于身之澡洁与否耳。尤翁代祝之说。恐难猝改。
设灵床条。既无魂帛。当废灵床。
灵床之设。本为尸柩尚在。象生而设也。既设灵床。故魂帛出入之。则灵床之设不设。盖在于尸柩之在不在。而不在于魂帛之有无也。改葬之礼。尸柩既出。则奉养象设。何可废也。至若有进无退。本以始葬而言。改葬既是变礼。则不可拘于常礼也明矣。且出柩后诸节。皆用始葬之仪。独于灵床。有此嫌耶。
祠土地条。祝文去神其佑之四字。
祠土地。将以求助于神也。去此四字。则不过告由之辞。而非求助之意也。与告庙祝辞无异。告庙与祠土体面自别。所告之祝。亦不可同辞。鄙意不必去之。
遣奠条。不设遣奠云云。
遣奠。宾飨之祭也。送行之终祭也。改葬不可无奠。有奠何可废遣奠。况且苞宲。用遣奠馀脯。则不行遣奠。何以宲苞。开元礼废祖奠而必行遣奠者。无或出于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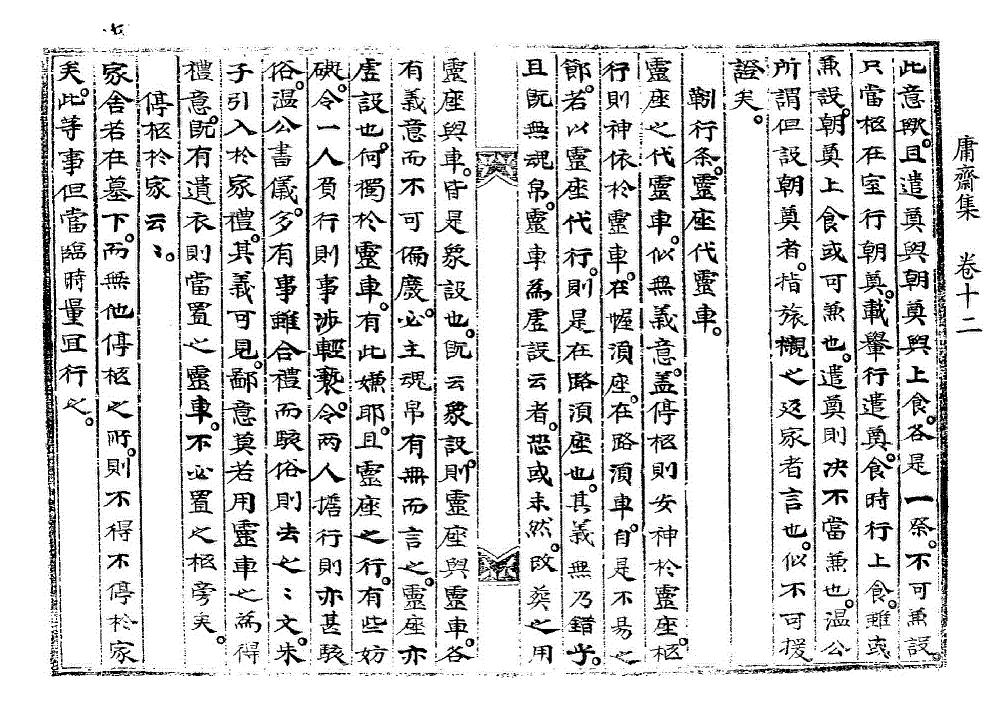 此意欤。且遣奠与朝奠与上食。各是一祭。不可兼设。只当柩在室行朝奠。载舆行遣奠。食时行上食。虽或兼设。朝奠上食或可兼也。遣奠则决不当兼也。温公所谓但设朝奠者。指旅榇之返家者言也。似不可援證矣。
此意欤。且遣奠与朝奠与上食。各是一祭。不可兼设。只当柩在室行朝奠。载舆行遣奠。食时行上食。虽或兼设。朝奠上食或可兼也。遣奠则决不当兼也。温公所谓但设朝奠者。指旅榇之返家者言也。似不可援證矣。靷行条。灵座代灵车。
灵座之代灵车。似无义意。盖停柩则安神于灵座。柩行则神依于灵车。在幄须座。在路须车。自是不易之节。若以灵座代行。则是在路须座也。其义无乃错乎。且既无魂帛。灵车为虚设云者。恐或未然。改葬之用灵座与车。皆是象设也。既云象设。则灵座与灵车。各有义意而不可偏废。必主魂帛有无而言之。灵座亦虚设也。何独于灵车。有此嫌耶。且灵座之行。有些妨碍。令一人负行则事涉轻亵。令两人担行则亦甚骇俗。温公书仪。多有事虽合礼而骇俗则去之之文。朱子引入于家礼。其义可见。鄙意莫若用灵车之为得礼意。既有遗衣则当置之灵车。不必置之柩旁矣。
停柩于家云云。
家舍若在墓下。而无他停柩之所。则不得不停于家矣。此等事但当临时量宜行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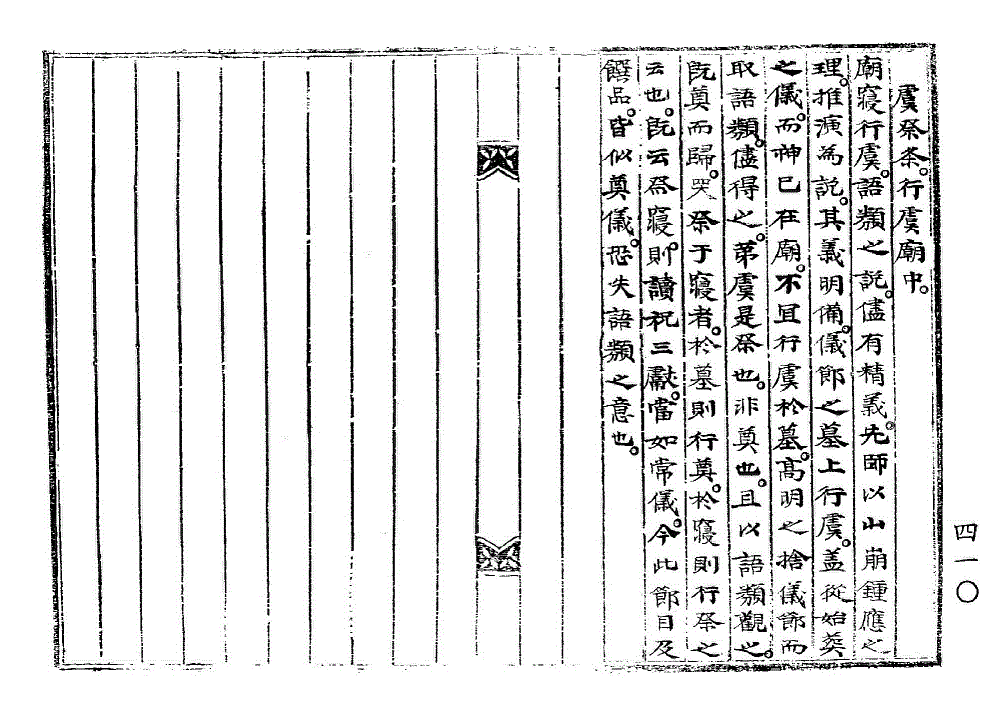 虞祭条。行虞庙中。
虞祭条。行虞庙中。庙寝行虞。语类之说。尽有精义。先师以山崩钟应之理。推演为说。其义明备。仪节之墓上行虞。盖从始葬之仪。而神已在庙。不宜行虞于墓。高明之舍仪节而取语类。尽得之。第虞是祭也。非奠也。且以语类观之。既奠而归。哭祭于寝者。于墓则行奠。于寝则行祭之云也。既云祭寝。则读祝三献。当如常仪。今此节目及馔品。皆似奠仪。恐失语类之意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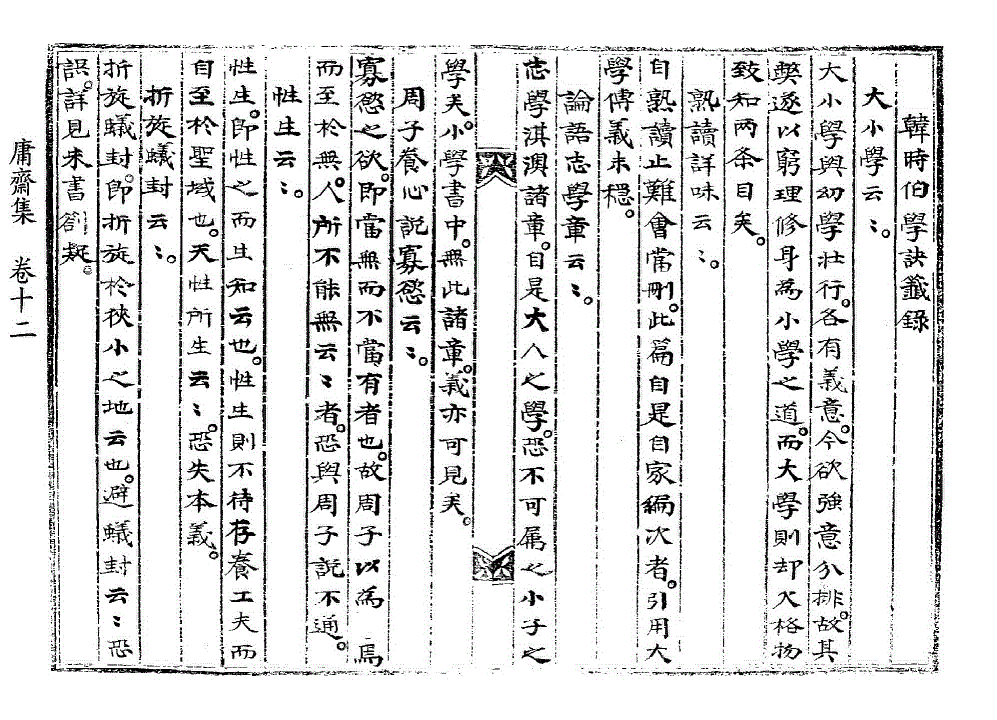 韩时伯学诀签录
韩时伯学诀签录大小学云云。
大小学与幼学壮行。各有义意。今欲强意分排。故其弊遂以穷理修身为小学之道。而大学则却欠格物致知两条目矣。
熟读详味云云。
自熟读止难会当删。此篇自是自家编次者。引用大学传义未稳。
论语志学章云云。
志学淇澳诸章。自是大人之学。恐不可属之小子之学矣。小学书中。无此诸章。义亦可见矣。
周子养心说寡欲云云。
寡欲之欲。即当无而不当有者也。故周子以为▣焉而至于无。人所不能无云云者。恐与周子说不通。
性生云云。
性生。即性之而生知云也。性生则不待存养工夫而自至于圣域也。天性所生云云。恐失本义。
折旋蚁封云云。
折旋蚁封。即折旋于狭小之地云也。避蚁封云云恐误。详见朱书劄疑。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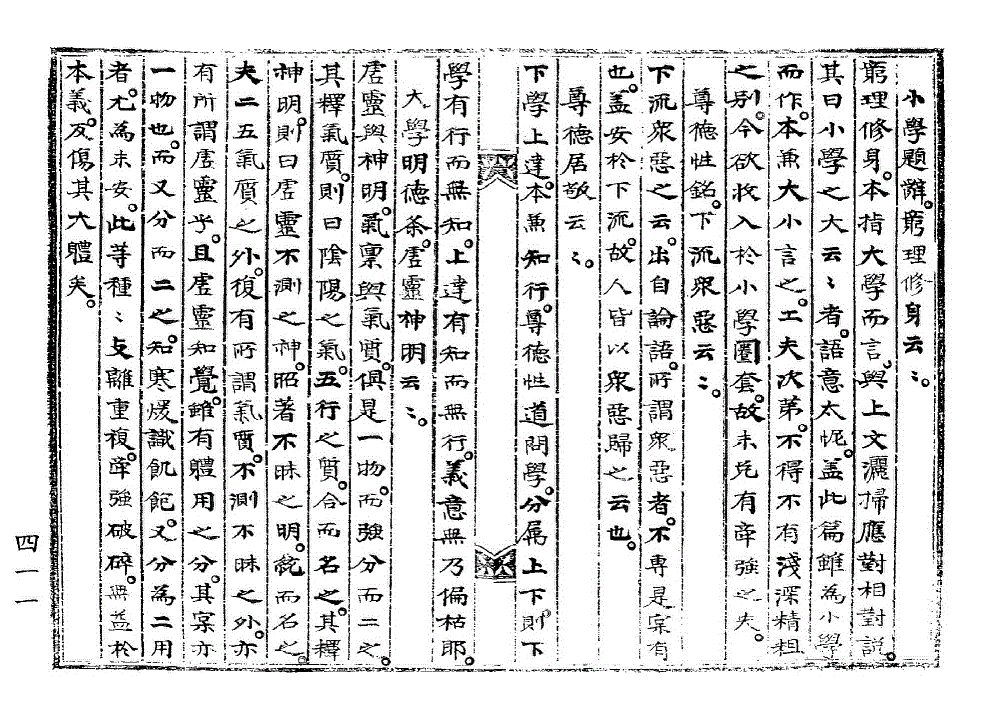 小学题辞。穷理修身云云。
小学题辞。穷理修身云云。穷理修身。本指大学而言。与上文洒扫应对相对说。其曰小学之大云云者。语意太怩。盖此篇虽为小学而作。本兼大小言之。工夫次第。不得不有浅深精粗之别。今欲收入于小学圈套。故未免有牵强之失。
尊德性铭。下流众恶云云。
下流众恶之云。出自论语。所谓众恶者。不专是宲有也。盖安于下流。故人皆以众恶归之云也。
尊德居敬云云。
下学上达。本兼知行。尊德性道问学。分属上下。则下学有行而无知。上达有知而无行。义意无乃偏枯耶。
大学明德条。虚灵神明云云。
虚灵与神明。气禀与气质。俱是一物。而强分而二之。其释气质。则曰阴阳之气。五行之质。合而名之。其释神明。则曰虚灵不测之神。昭著不昧之明。统而名之。夫二五气质之外。复有所谓气质。不测不昧之外。亦有所谓虚灵乎。且虚灵知觉。虽有体用之分。其宲亦一物也。而又分而二之。知寒煖识饥饱。又分为二用者。尤为未安。此等种种支离重复。牵强破碎。无益于本义。反伤其大体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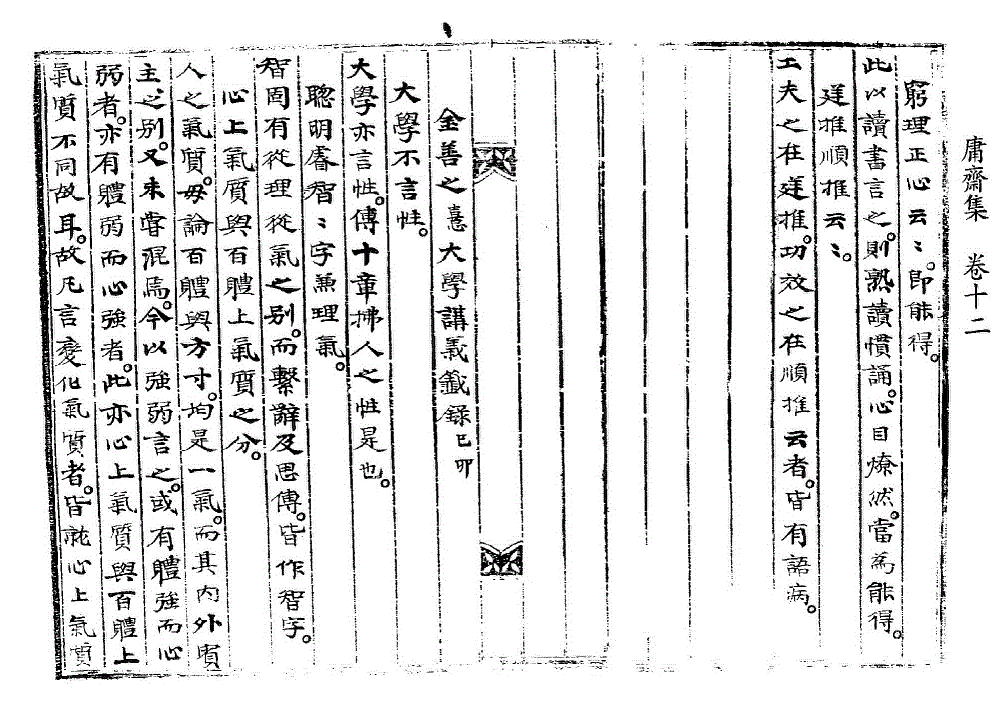 穷理正心云云。即能得。
穷理正心云云。即能得。此以读书言之。则熟读惯诵。心目燎然。当为能得。
逆推顺推云云。
工夫之在逆推。功效之在顺推云者。皆有语病。
金善之(憙)大学讲义签录(己卯)
大学不言性。
大学亦言性。传十章拂人之性是也。
聪明睿智智字兼理气。
智固有从理从气之别。而系辞及思传。皆作智字。
心上气质与百体上气质之分。
人之气质。毋论百体与方寸。均是一气。而其内外宾主之别。又未尝混焉。今以强弱言之。或有体强而心弱者。亦有体弱而心强者。此亦心上气质与百体上气质不同故耳。故凡言变化气质者。皆就心上气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2L 页
 言之。至于百体上气质。则一定而不可变化。此义见于栗谷要诀。
言之。至于百体上气质。则一定而不可变化。此义见于栗谷要诀。聪明属心
聪明有从血气而言者。有从义理而言者。师旷之聪。离娄之明。血气之聪明也。血气之聪明属耳目。随血气而盛衰。故虽在圣人分上。未免有老壮之别。义理之聪明属心。随义理而通塞。故君子通小人塞。而无间于老少。系辞及思传所谓聪明。皆从义理而言者。故俱属于心。若以耳目之管涉于心而以聪明属心。则四肢百体。孰不管涉于心乎。如是说出。恐或窒碍。
君师之别。
君师之为一。序文之义甚明。治而教之两字。可见一人兼行之意。
补阙为传五章。
补阙东西看亦可也。至于意字。明有归属。决不两边主说。使人疑眩。
明明德于天下。兼民己言。
使之明之者。己之事也。以是谓之兼民己则可也。而直指明德而谓兼民己。则恐非章句之义。章句明其之其即民也。其与明德。不可差殊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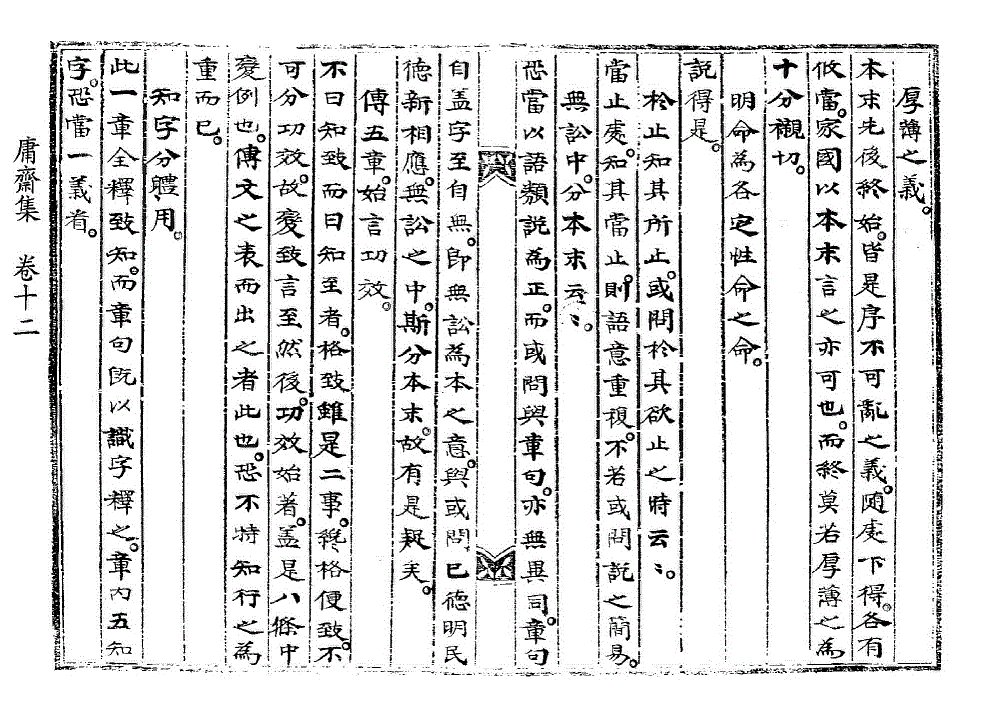 厚薄之义。
厚薄之义。本末先后终始。皆是序不可乱之义。随处下得。各有攸当。家国以本末言之亦可也。而终莫若厚薄之为十分衬切。
明命为各定性命之命。
说得是。
于止知其所止。或问于其欲止之时云云。
当止处。知其当止。则语意重复。不若或问说之简易。
无讼中。分本末云云。
恐当以语类说为正。而或问与章句。亦无异同。章句自盖字至自无。即无讼为本之意。与或问己德明民德新相应。无讼之中。斯分本末。故有是疑矣。
传五章。始言功效。
不曰知致而曰知至者。格致虽是二事。才格便致。不可分功效。故变致言至然后。功效始著。盖是八条中变例也。传文之表而出之者此也。恐不特知行之为重而已。
知字分体用。
此一章全释致知。而章句既以识字释之。章内五知字。恐当一义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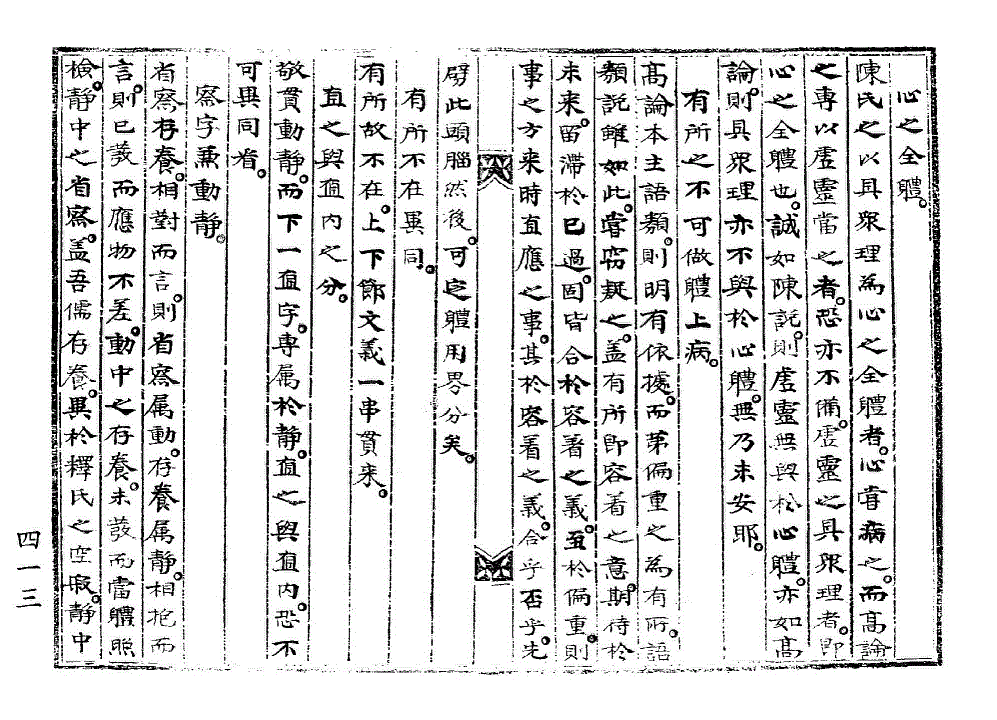 心之全体。
心之全体。陈氏之以具众理为心之全体者。心尝病之。而高论之专以虚灵当之者。恐亦不备。虚灵之具众理者。即心之全体也。诚如陈说。则虚灵无与于心体。亦如高论。则具众理亦不与于心体。无乃未安耶。
有所之不可做体上病。
高论本主语类。则明有依据。而第偏重之为有所。语类说虽如此。尝窃疑之。盖有所即容着之意。期待于未来。留滞于己过。固皆合于容着之义。至于偏重。则事之方来时直应之事。其于容着之义。合乎否乎。先劈此头脑然后。可定体用界分矣。
有所不在异同。
有所故不在。上下节文义一串贯来。
直之与直内之分。
敬贯动静。而下一直字。专属于静。直之与直内。恐不可异同看。
察字兼动静。
省察存养。相对而言。则省察属动。存养属静。相抱而言。则已发而应物不差。动中之存养。未发而当体照检。静中之省察。盖吾儒存养。异于释氏之空寂。静中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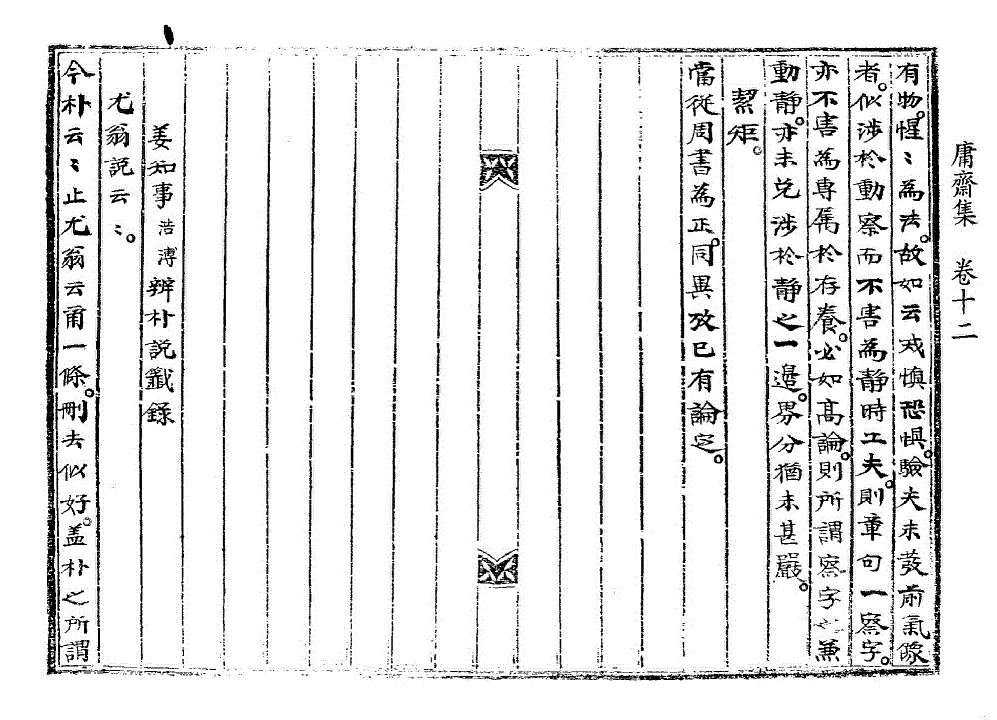 有物。惺惺为法。故如云戒慎恐惧。验夫未发前气像者。似涉于动察而不害为静时工夫。则章句一察字。亦不害为专属于存养。必如高论。则所谓察字之兼动静。亦未免涉于静之一边。界分犹未甚严。
有物。惺惺为法。故如云戒慎恐惧。验夫未发前气像者。似涉于动察而不害为静时工夫。则章句一察字。亦不害为专属于存养。必如高论。则所谓察字之兼动静。亦未免涉于静之一边。界分犹未甚严。絜矩。
当从周书为正。同异考已有论定。
姜知事(浩溥)辨朴说签录
尤翁说云云。
今朴云云止尤翁云尔一条。删去似好。盖朴之所谓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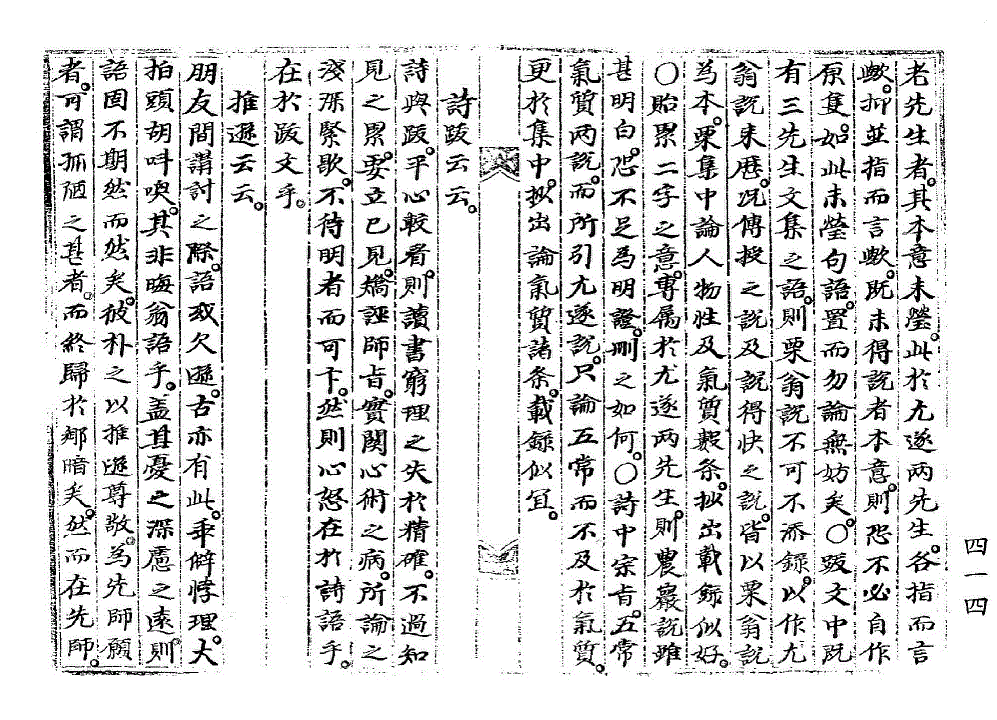 老先生者。其本意未莹。此于尤遂两先生。各指而言欤。抑并指而言欤。既未得说者本意。则恐不必自作原只。如此未莹句语。置而勿论无妨矣。○跋文中既有三先生文集之语。则栗翁说不可不添录。以作尤翁说来历。况传授之说及说得快之说。皆以栗翁说为本。栗集中论人物性及气质数条。抄出载录似好。○贻累二字之意。专属于尤遂两先生。则农岩说虽甚明白。恐不足为明證。删之如何。○诗中宗旨。五常气质两说。而所引尤遂说。只论五常而不及于气质。更于集中。抄出论气质诸条。载录似宜。
老先生者。其本意未莹。此于尤遂两先生。各指而言欤。抑并指而言欤。既未得说者本意。则恐不必自作原只。如此未莹句语。置而勿论无妨矣。○跋文中既有三先生文集之语。则栗翁说不可不添录。以作尤翁说来历。况传授之说及说得快之说。皆以栗翁说为本。栗集中论人物性及气质数条。抄出载录似好。○贻累二字之意。专属于尤遂两先生。则农岩说虽甚明白。恐不足为明證。删之如何。○诗中宗旨。五常气质两说。而所引尤遂说。只论五常而不及于气质。更于集中。抄出论气质诸条。载录似宜。诗跋云云。
诗与跋。平心较看。则读书穷理之失于精确。不过知见之累。要立己见。矫诬师旨。实关心术之病。所论之浅深紧歇。不待明者而可卞。然则心怒在于诗语乎。在于跋文乎。
推逊云云。
朋友间讲讨之际。语或欠逊。古亦有此。乖僻悖理。大拍头胡叫唤。其非晦翁语乎。盖其忧之深虑之远。则语固不期然而然矣。彼朴之以推逊尊敬。为先师愿者。可谓孤陋之甚者。而终归于乡暗矣。然而在先师。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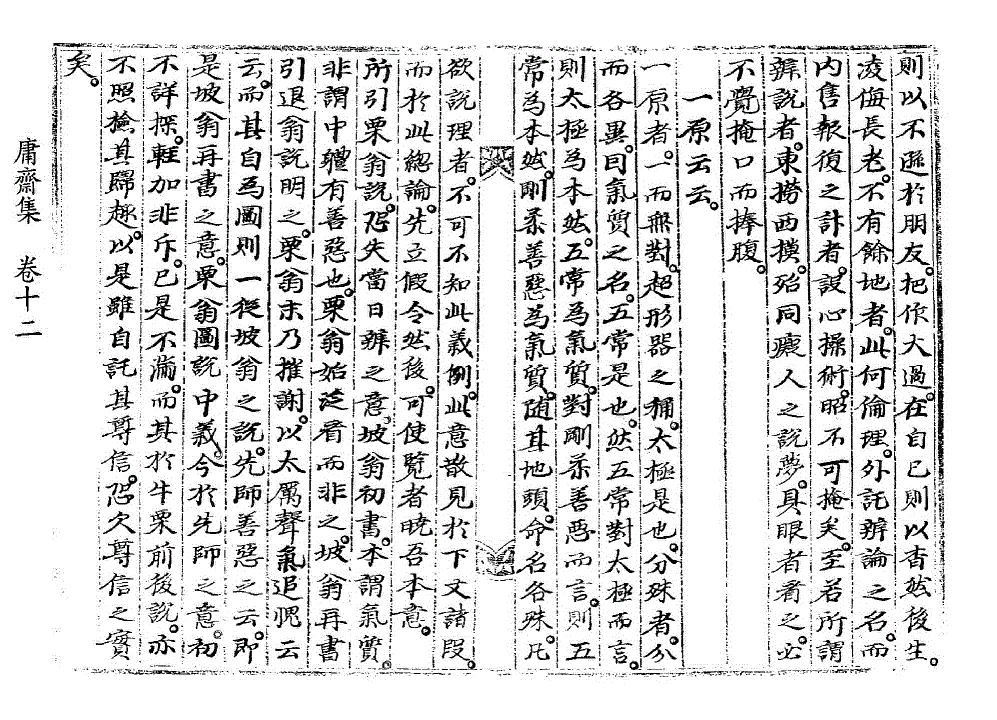 则以不逊于朋友。把作大过。在自己则以杳然后生。凌侮长老。不有馀地者。此何伦理。外托辨论之名。而内售报复之计者。设心操术。昭不可掩矣。至若所谓辨说者。东捞西摸。殆同痴人之说梦。具眼者看之。必不觉掩口而捧腹。
则以不逊于朋友。把作大过。在自己则以杳然后生。凌侮长老。不有馀地者。此何伦理。外托辨论之名。而内售报复之计者。设心操术。昭不可掩矣。至若所谓辨说者。东捞西摸。殆同痴人之说梦。具眼者看之。必不觉掩口而捧腹。一原云云。
一原者。一而无对。超形器之称。太极是也。分殊者。分而各异。因气质之名。五常是也。然五常对太极而言。则太极为本然。五常为气质。对刚柔善恶而言。则五常为本然。刚柔善恶为气质。随其地头。命名各殊。凡欲说理者。不可不知此义例。此意散见于下文诸段。而于此总论。先立假令然后。可使览者晓吾本意。
所引栗翁说。恐失当日辨之意。坡翁初书。本谓气质。非谓中体有善恶也。栗翁始泛看而非之。坡翁再书引退翁说明之。栗翁末乃摧谢。以太厉声气追愧云云。而其自为图则一从坡翁之说。先师善恶之云。即是坡翁再书之意。栗翁图说中义。今于先师之意。初不详探。轻加非斥。已是不满。而其于牛栗前后说。亦不照检其归趣。以是虽自托其尊信。恐欠尊信之实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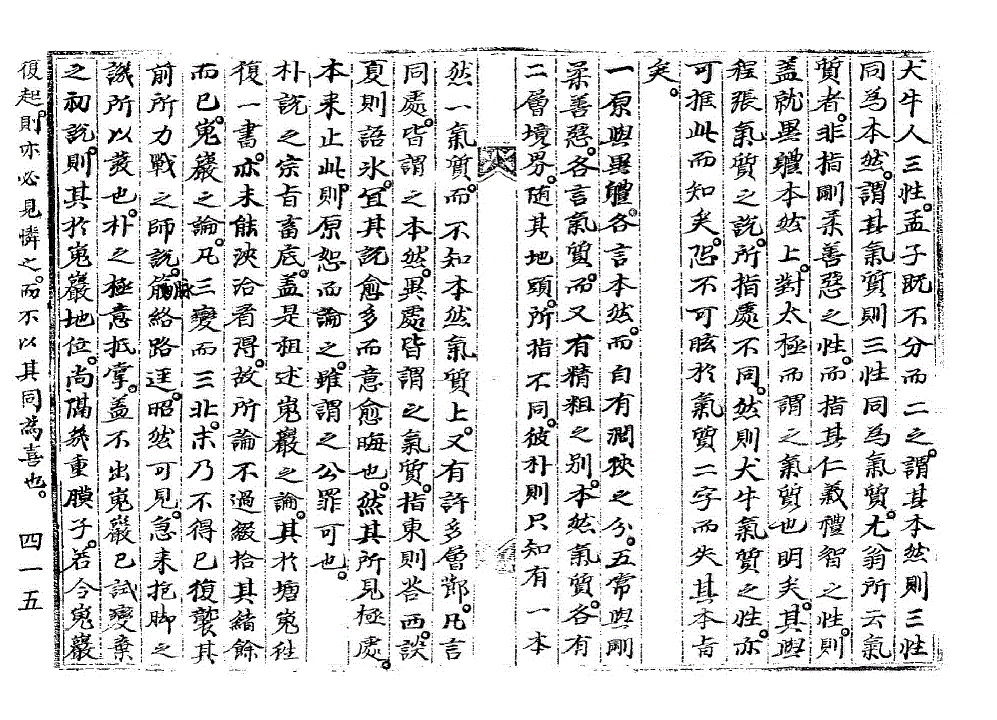 犬牛人三性。孟子既不分而二之。谓其本然则三性同为本然。谓其气质则三性同为气质。尤翁所云气质者。非指刚柔善恶之性。而指其仁义礼智之性。则盖就异体本然上。对太极而谓之气质也明矣。其与程张气质之说。所指处不同。然则犬牛气质之性。亦可推此而知矣。恐不可眩于气质二字而失其本旨矣。
犬牛人三性。孟子既不分而二之。谓其本然则三性同为本然。谓其气质则三性同为气质。尤翁所云气质者。非指刚柔善恶之性。而指其仁义礼智之性。则盖就异体本然上。对太极而谓之气质也明矣。其与程张气质之说。所指处不同。然则犬牛气质之性。亦可推此而知矣。恐不可眩于气质二字而失其本旨矣。一原与异体。各言本然。而自有阔狭之分。五常与刚柔善恶。各言气质。而又有精粗之别。本然气质。各有二层境界。随其地头。所指不同。彼朴则只知有一本然一气质。而不知本然气质上。又有许多层节。凡言同处。皆谓之本然。异处皆谓之气质。指东则答西。谈夏则语冰。宜其说愈多而意愈晦也。然其所见极处。本来止此。则原恕而论之。虽谓之公罪可也。
朴说之宗旨畜底。盖是祖述嵬岩之论。其于塘嵬往复一书。亦未能浃洽看得。故所论不过缀拾其绪馀而已。嵬岩之论。凡三变而三北。末乃不得已复袭其前所力战之师说。脉络路径。昭然可见。急来抱脚之讥所以发也。朴之极意抵掌。盖不出嵬岩已试变弃之初说。则其于嵬岩地位。尚隔几重膜子。若令嵬岩复起。则亦必见怜之。而不以其同为喜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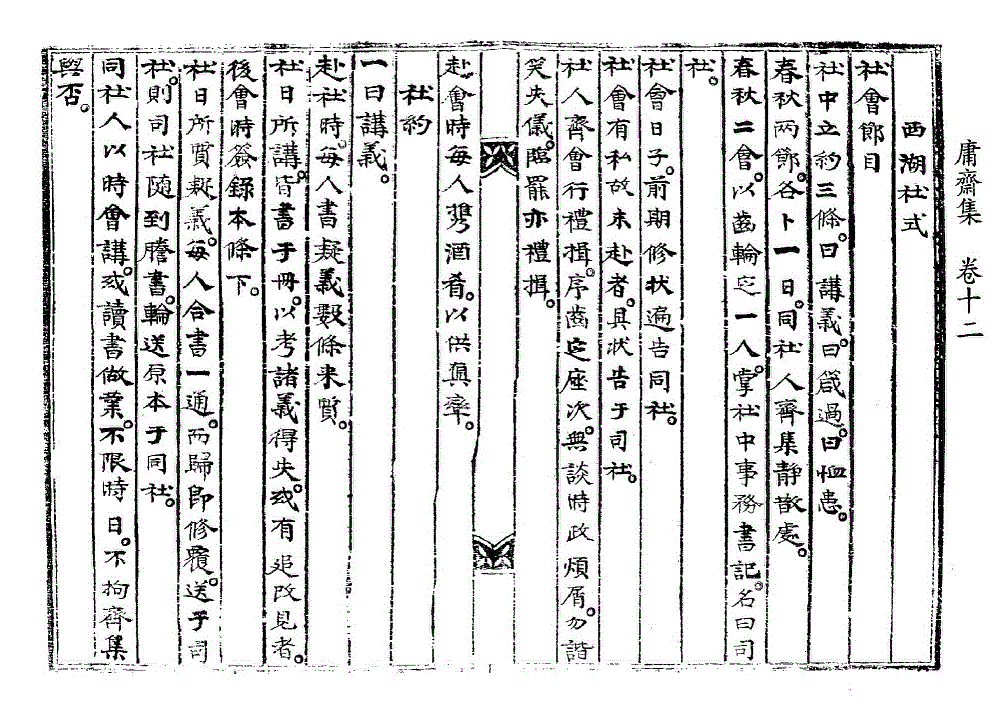 西湖社式
西湖社式社会节目
社中立约三条。曰讲义。曰箴过。曰恤患。
春秋两节。各卜一日。同社人齐集静散处。
春秋二会。以齿轮定一人。掌社中事务书记。名曰司社。
社会日子。前期修状遍告同社。
社会有私故未赴者。具状告于司社。
社人齐会行礼揖。序齿定座次。无谈时政烦屑。勿谐笑失仪。临罢亦礼揖。
赴会时每人携酒肴。以供真率。
社约
一曰讲义。
赴社时。每人书疑义数条来质。
社日所讲。皆书于册。以考诸义得失。或有追改见者。后会时签录本条下。
社日所质疑义。每人合书一通。而归即修覆。送于司社。则司社随到誊书。轮送原本于同社。
同社人以时会讲。或读书做业。不限时日。不拘齐集与否。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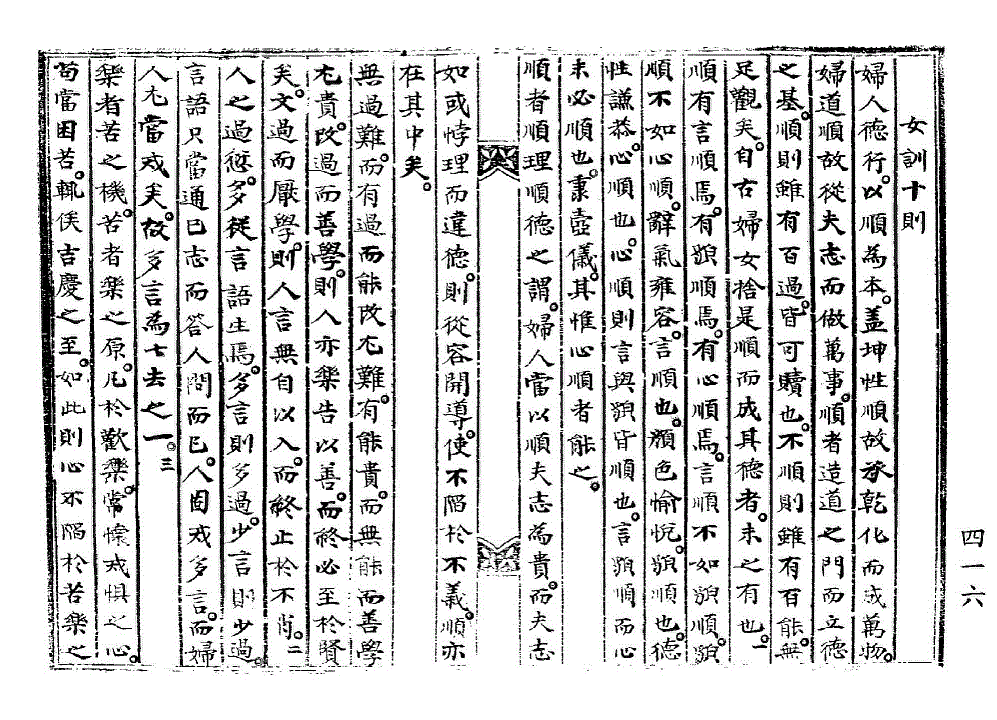 女训十则
女训十则妇人德行。以顺为本。盖坤性顺故承乾化而成万物。妇道顺故从夫志而做万事。顺者造道之门而立德之基。顺则虽有百过。皆可赎也。不顺则虽有百能。无足观矣。自古妇女舍是顺而成其德者。未之有也。(一)
顺有言顺焉。有貌顺焉。有心顺焉。言顺不如貌顺。貌顺不如心顺。辞气雍容。言顺也。颜色愉悦。貌顺也。德性谦恭。心顺也。心顺则言与貌皆顺也。言貌顺而心未必顺也。秉壸仪。其惟心顺者能之。
顺者顺理顺德之谓。妇人当以顺夫志为贵。而夫志如或悖理而违德。则从容开导。使不陷于不义。顺亦在其中矣。
无过难。而有过而能改尤难。有能贵。而无能而善学尤贵。改过而善学。则人亦乐告以善。而终必至于贤矣。文过而厌学。则人言无自以入。而终止于不肖。(二)
人之过愆。多从言语生焉。多言则多过。少言则少过。言语只当通己志而答人问而已。人固戒多言。而妇人尤当戒矣。故多言为七去之一。(三)
乐者苦之机。苦者乐之原。凡于欢乐。常怀戒惧之心。苟当困苦。辄俟吉庆之至。如此则心不陷于苦乐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7H 页
 中。而偏性亦自宽安矣。(四)
中。而偏性亦自宽安矣。(四)浮谤之来。一切勿辨。被人苦诘。只答以终或有知。胜于极口分疏。人言亦自起自灭。(五)
宁为过恭。毋或少傲。宁为过弱。毋或少刚。宁为过拙。毋或少巧。宁为过讷。毋或少辩。秉心和平。律己庄严。接物乐易。五福攸会。九族归仁。(六)
见可于舅姑夫子。无或自弛。益思所以无过。见不是于舅姑夫子。无或怀怨。益思所以起敬。然而要当尽吾分而已。亦勿以诡道枉行。干誉而避毁。
处妯娌娣姒之间。虚心恭己。量力效劳。务得其和乐。(七)
奉祭祀接宾客。责在内政。享先则务尽诚敬。待人则曲有情款。勿以家力之乏供具之劳。少有懈意与苦色。(八)
教子之方。在于蒙养。必自孩提。勿示慈爱之色。严加摧抑。常令屈意于长者。(九)
婢仆代我劳者也。待之不可贱薄。以身体之。轸其饥寒。均其劳逸。宁废己事。不可以己所不堪加之。
男女之际。大嫌存焉。同席共食。戒自七岁。虽于同气至亲。不可昵居而杂处。(十)
妇人恶行。莫甚于嫉妒。妒者欲其专夫之宠也。苟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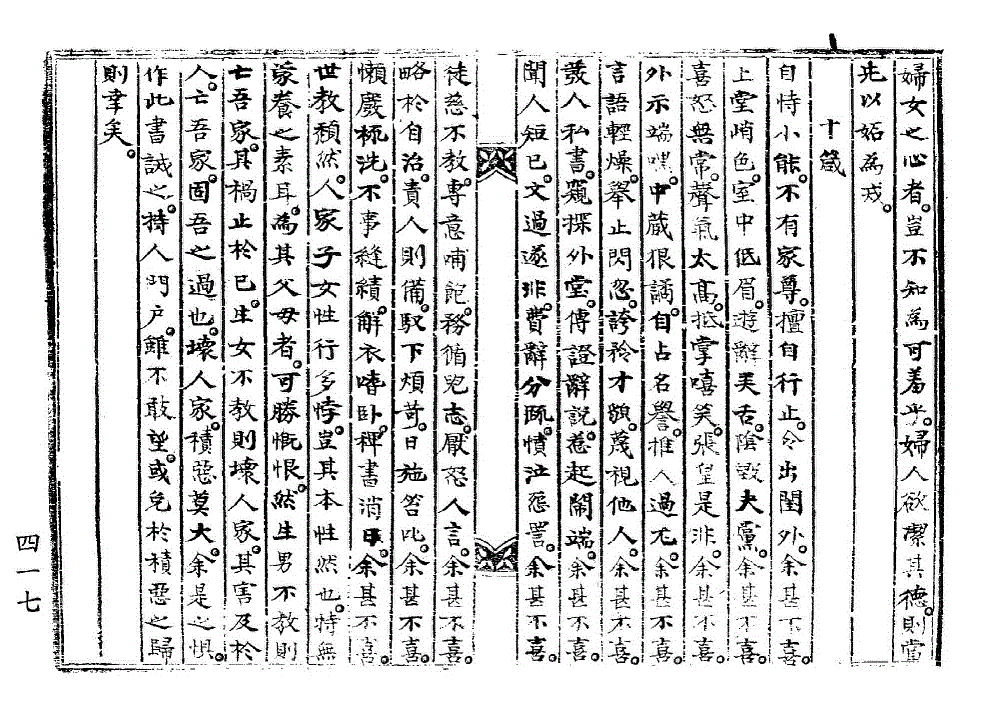 妇女之心者。岂不知为可羞乎。妇人欲洁其德。则当先以妒为戒。
妇女之心者。岂不知为可羞乎。妇人欲洁其德。则当先以妒为戒。十箴
自恃小能。不有家尊。擅自行止。令出闺外。余甚不喜。
上堂峭色。室中低眉。游辞弄舌。阴毁夫党。余甚不喜。
喜怒无常。声气太高。抵掌嘻笑。张皇是非。余甚不喜。
外示端嘿。中藏狠谲。自占名誉。推人过尤。余甚不喜。
言语轻燥。举止闪忽。誇矜才貌。蔑视他人。余甚不喜。
发人私书。窥探外堂。传證辞说。惹起闹端。余甚不喜。
闻人短己。文过遂非。费辞分疏。愤泣怨詈。余甚不喜。
徒慈不教。专意哺饱。务循儿志。厌怒人言。余甚不喜。
略于自治。责人则备。驭下烦苛。日施笞比。余甚不喜。
懒废梳洗。不事缝绩。解衣嗜卧。稗书消日。余甚不喜。
世教颓然。人家子女性行多悖。岂其本性然也。特无蒙养之素耳。为其父母者。可胜慨恨。然生男不教则亡吾家。其祸止于己。生女不教则坏人家。其害及于人。亡吾家。固吾之过也。坏人家。积恶莫大。余是之惧。作此书诫之。持人门户。虽不敢望。或免于积恶之归则幸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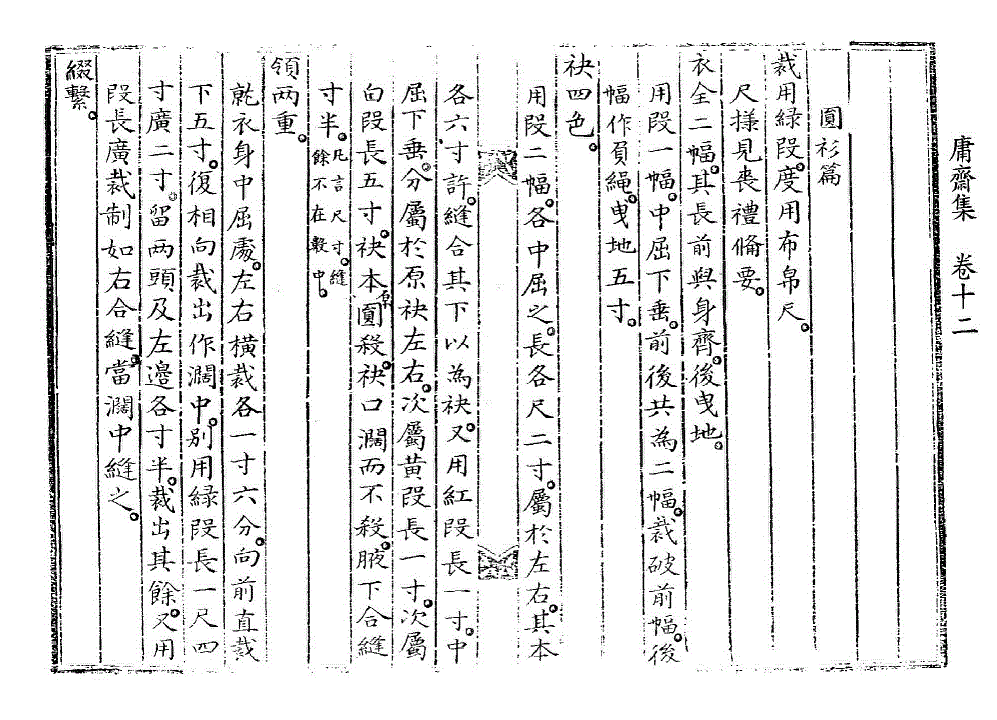 圆衫篇
圆衫篇裁用绿段。度用布帛尺。
尺㨾见丧礼备要。
衣全二幅。其长前与身齐。后曳地。
用段一幅。中屈下垂。前后共为二幅。裁破前幅。后幅作负绳。曳地五寸。
袂四色。
用段二幅。各中屈之。长各尺二寸。属于左右。其本各六寸许。缝合其下以为袂。又用红段长一寸。中屈下垂。分属于原袂左右。次属黄段长一寸。次属白段长五寸。袂本原圆杀。袂口𤄃而不杀。腋下合缝寸半。(凡言尺寸。缝馀不在数中。)
领两重。
就衣身中屈处。左右横裁各一寸六分。向前直裁下五寸。复相向裁出作𤄃中。别用绿段长一尺四寸广二寸。留两头及左边各寸半。裁出其馀。又用段长广裁制如右合缝。当𤄃中缝之。
缀系。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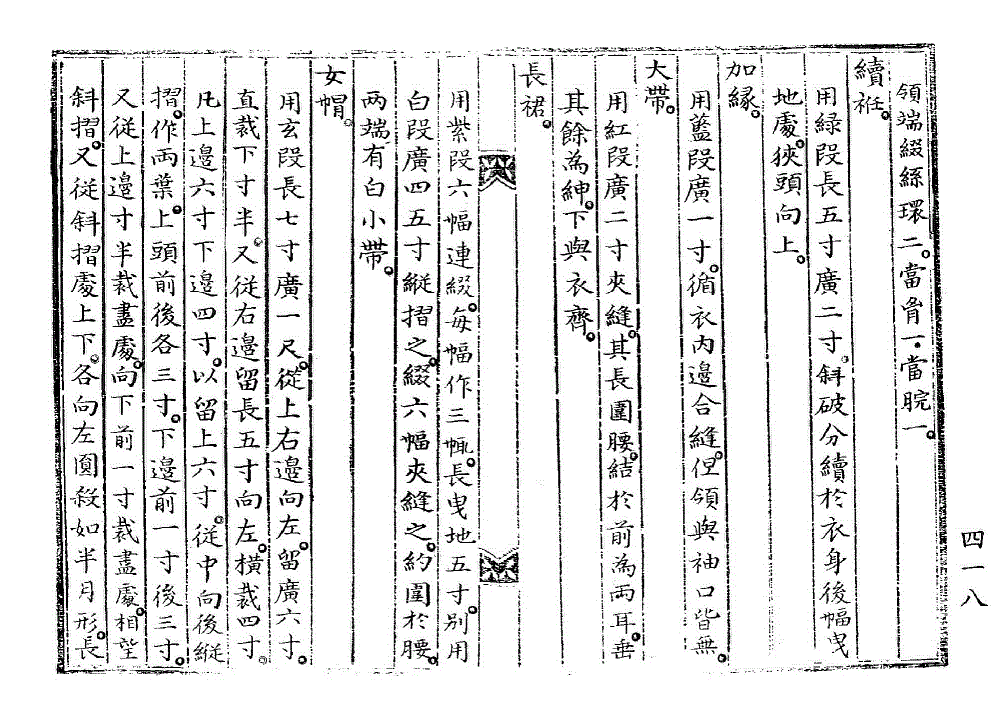 领端缀丝环二。当胸一,当脘一。
领端缀丝环二。当胸一,当脘一。续衽。
用绿段长五寸广二寸。斜破分续于衣身后幅曳地处。狭头向上。
加缘。
用蓝段广一寸。循衣内边合缝。但领与袖口皆无。
大带。
用红段广二寸夹缝。其长围腰。结于前为两耳。垂其馀为绅。下与衣齐。
长裙。
用紫段六幅连缀。每幅作三㡇。长曳地五寸。别用白段广四五寸纵摺之。缀六幅夹缝之。约围于腰。两端有白小带。
女帽。
用玄段长七寸广一尺。从上右边向左。留广六寸。直裁下寸半。又从右边留长五寸向左。横裁四寸。凡上边六寸下边四寸。以留上六寸。从中向后纵摺。作两叶。上头前后各三寸。下边前一寸后三寸。又从上边寸半裁尽处。向下前一寸裁尽处。相望斜摺。又从斜摺处上下。各向左圆杀如半月形。长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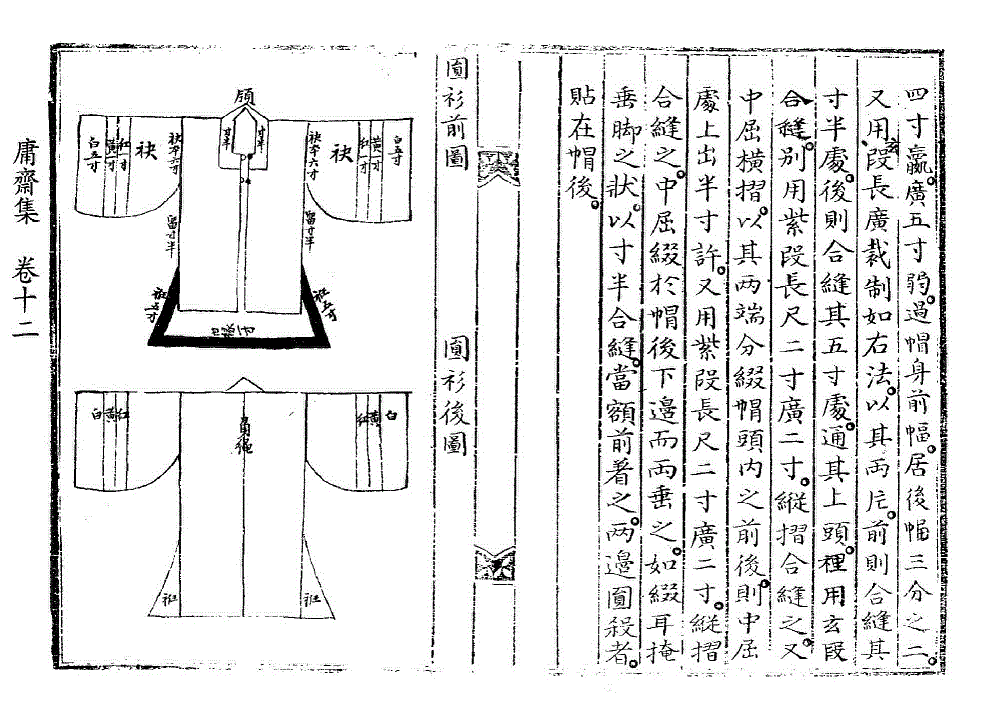 四寸嬴。广五寸弱。过帽身前幅。居后幅三分之二。又用玄段长广裁制如右法。以其两片。前则合缝其寸半处。后则合缝其五寸处。通其上头。里用玄段合缝。别用紫段长尺二寸广二寸。纵摺合缝之。又中屈横摺。以其两端分缀帽头内之前后。则中屈处上出半寸许。又用紫段长尺二寸广二寸。纵摺合缝之。中屈缀于帽后下边而两垂之。如缀耳掩垂脚之状。以寸半合缝。当额前着之。两边圆杀者。贴在帽后。
四寸嬴。广五寸弱。过帽身前幅。居后幅三分之二。又用玄段长广裁制如右法。以其两片。前则合缝其寸半处。后则合缝其五寸处。通其上头。里用玄段合缝。别用紫段长尺二寸广二寸。纵摺合缝之。又中屈横摺。以其两端分缀帽头内之前后。则中屈处上出半寸许。又用紫段长尺二寸广二寸。纵摺合缝之。中屈缀于帽后下边而两垂之。如缀耳掩垂脚之状。以寸半合缝。当额前着之。两边圆杀者。贴在帽后。圆衫前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圆衫后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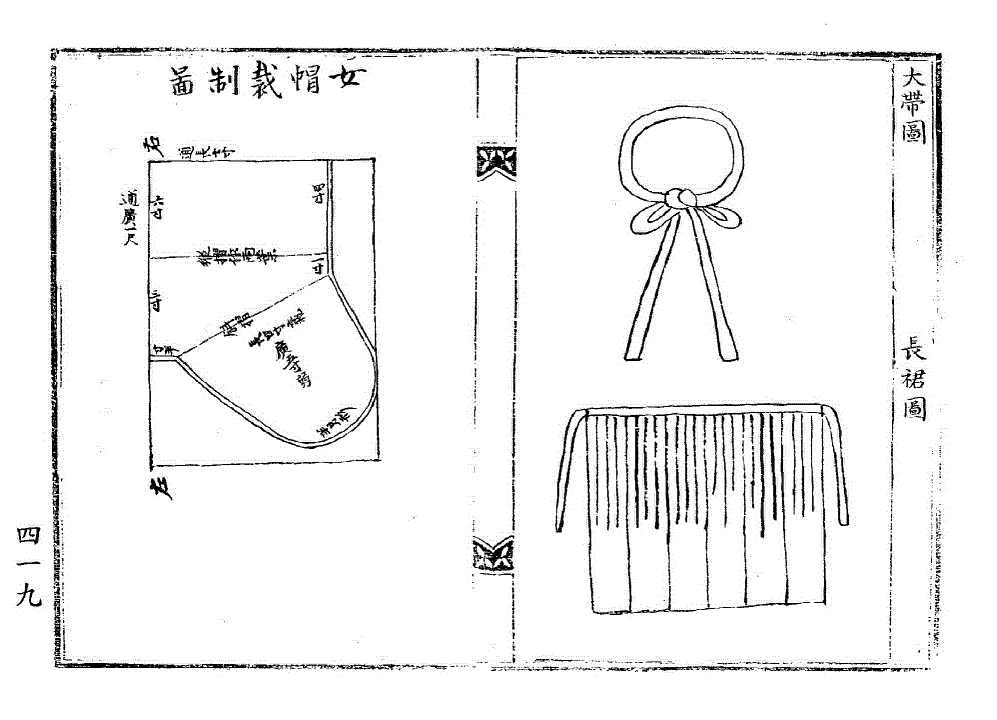 大带图
大带图삽화 새창열기
长裙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裁制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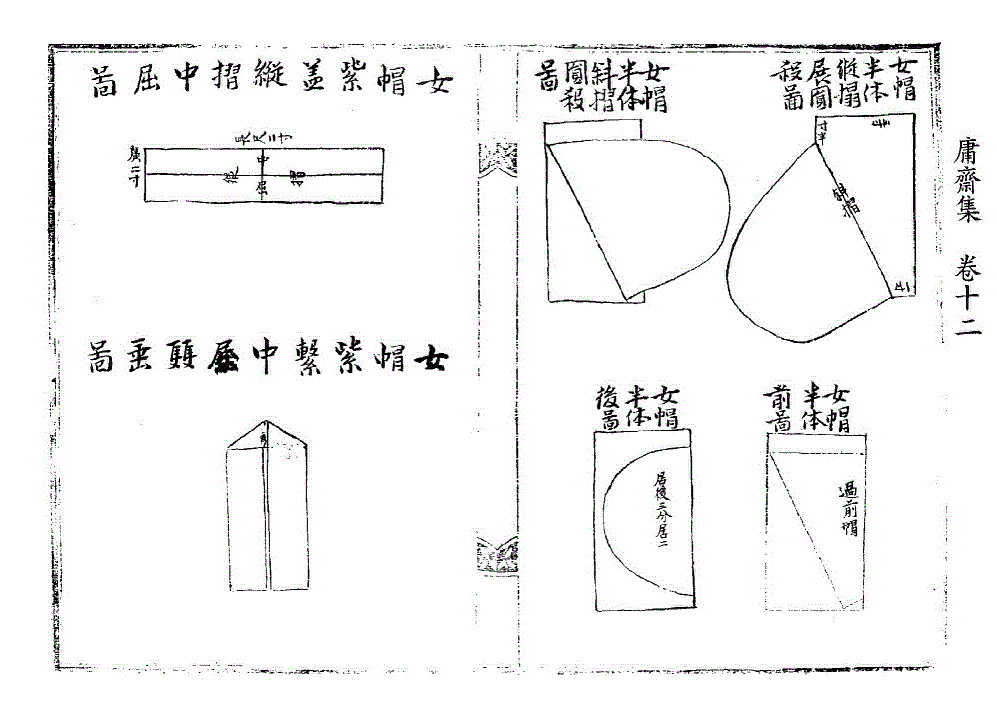 女帽半体纵拓(一作摺)展圆杀图
女帽半体纵拓(一作摺)展圆杀图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半体斜摺圆杀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半体前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半体后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紫盖纵摺中屈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紫系中屈双垂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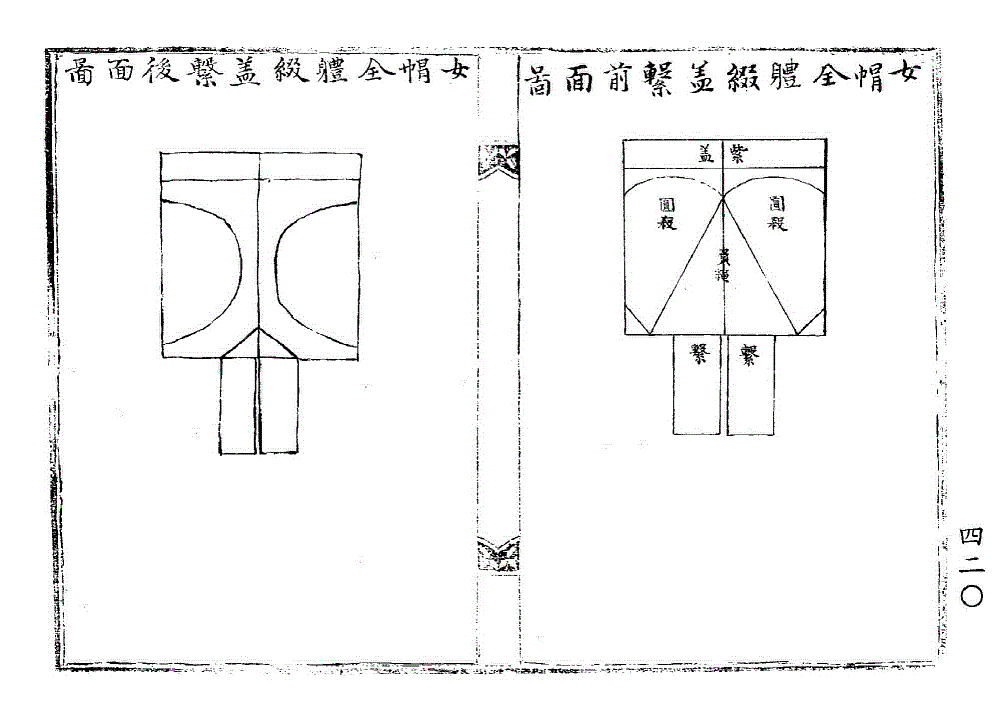 女帽全体缀盖系前面图
女帽全体缀盖系前面图삽화 새창열기
女帽全体缀盖系后面图
삽화 새창열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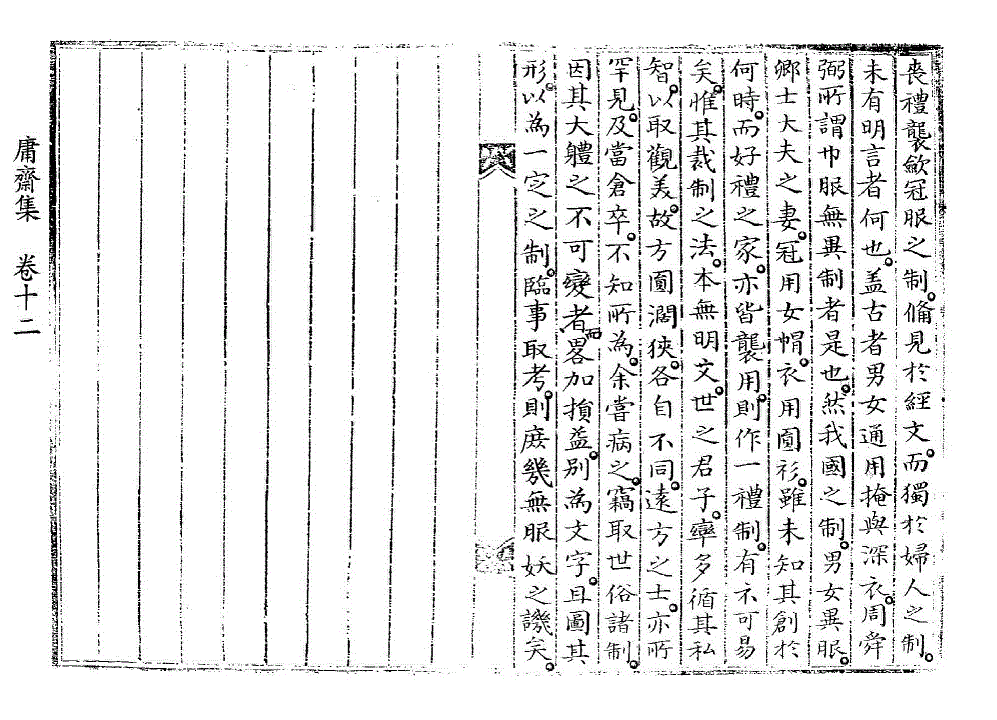 丧礼袭敛冠服之制。备见于经文。而独于妇人之制。未有明言者何也。盖古者男女通用掩与深衣。周舜弼所谓巾服无异制者是也。然我国之制。男女异服。卿士大夫之妻。冠用女帽。衣用圆衫。虽未知其创于何时。而好礼之家。亦皆袭用。则作一礼制。有不可易矣。惟其裁制之法。本无明文。世之君子。率多循其私智。以取观美。故方圆阔狭。各自不同。远方之士。亦所罕见。及当仓卒。不知所为。余尝病之。窃取世俗诸制。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略加损益。别为文字。且图其形。以为一定之制。临事取考。则庶几无服妖之讥矣。
丧礼袭敛冠服之制。备见于经文。而独于妇人之制。未有明言者何也。盖古者男女通用掩与深衣。周舜弼所谓巾服无异制者是也。然我国之制。男女异服。卿士大夫之妻。冠用女帽。衣用圆衫。虽未知其创于何时。而好礼之家。亦皆袭用。则作一礼制。有不可易矣。惟其裁制之法。本无明文。世之君子。率多循其私智。以取观美。故方圆阔狭。各自不同。远方之士。亦所罕见。及当仓卒。不知所为。余尝病之。窃取世俗诸制。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略加损益。别为文字。且图其形。以为一定之制。临事取考。则庶几无服妖之讥矣。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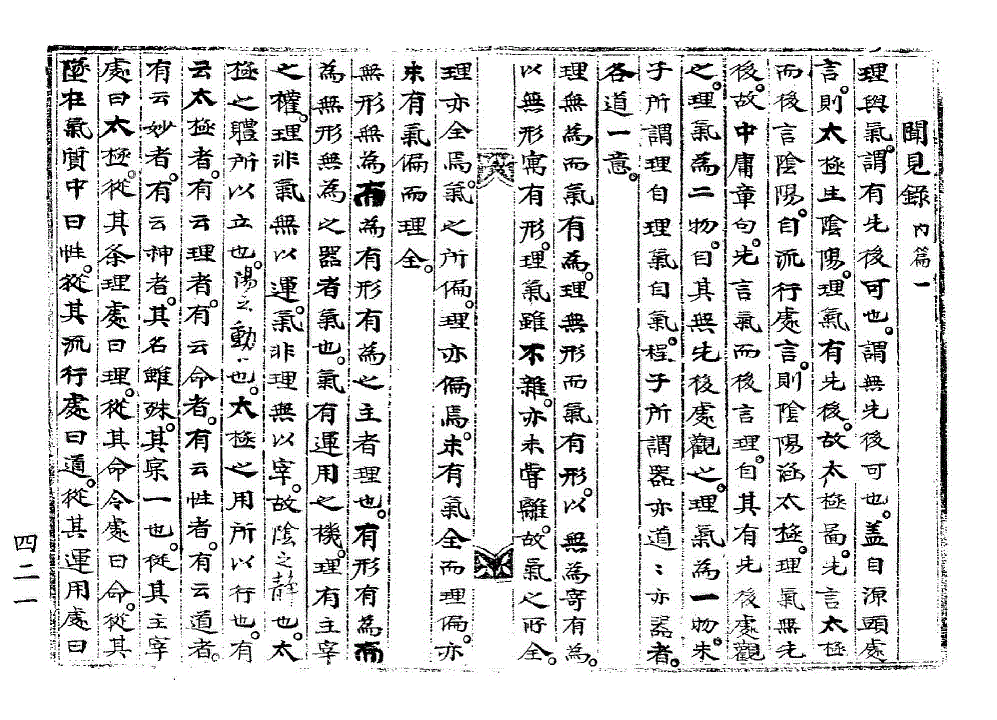 闻见录(内篇一)
闻见录(内篇一)理与气。谓有先后可也。谓无先后可也。盖自源头处言。则太极生阴阳。理气有先后。故太极啚。先言太极而后言阴阳。自流行处言。则阴阳涵太极。理气无先后。故中庸章句。先言气而后言理。自其有先后处观之。理气为二物。自其无先后处观之。理气为一物。朱子所谓理自理气自气。程子所谓器亦道道亦器者。各道一意。
理无为而气有为。理无形而气有形。以无为寄有为。以无形寓有形。理气虽不杂。亦未尝离。故气之所全。理亦全焉。气之所偏。理亦偏焉。未有气全而理偏。亦未有气偏而理全。
无形无为而为有形有为之主者理也。有形有为而为无形无为之器者气也。气有运用之机。理有主宰之权。理非气无以运。气非理无以宰。故阴之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阳之动也。太极之用所以行也。有云太极者。有云理者。有云命者。有云性者。有云道者。有云妙者。有云神者。其名虽殊。其宲一也。从其主宰处曰太极。从其条理处曰理。从其命令处曰命。从其坠在气质中曰性。从其流行处曰道。从其运用处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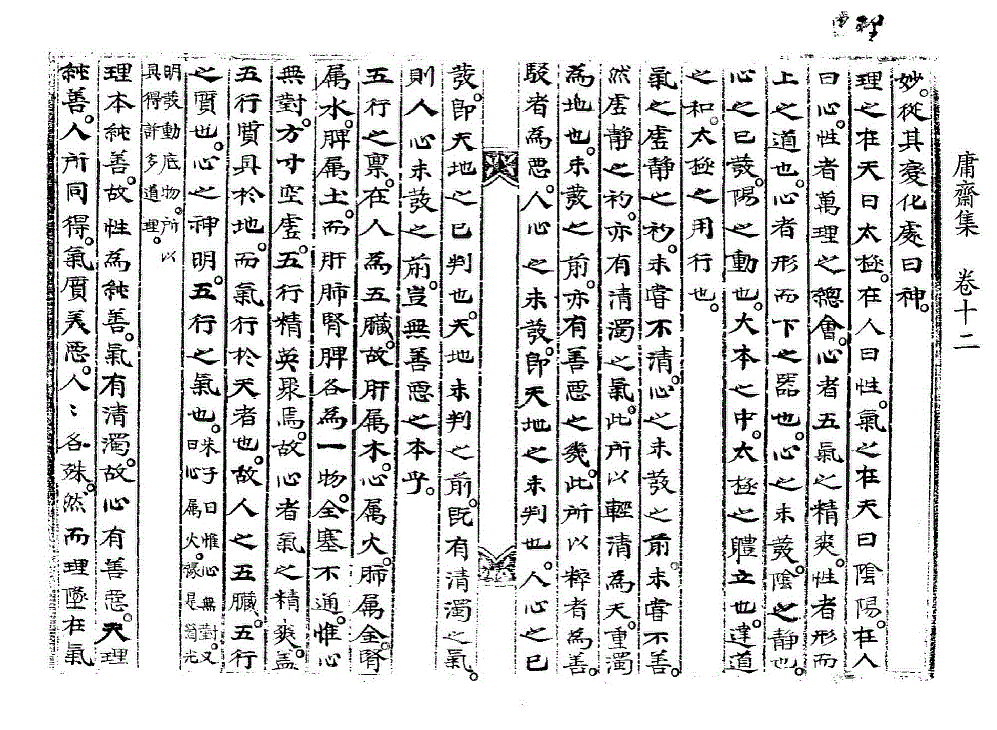 妙。从其变化处曰神。
妙。从其变化处曰神。理之在天曰太极。在人曰性。气之在天曰阴阳。在人曰心。性者万理之总会。心者五气之精爽。性者形而上之道也。心者形而下之器也。心之未发。阴之静也。心之已发。阳之动也。大本之中。太极之体立也。达道之和。太极之用行也。
气之虚静之初。未尝不清。心之未发之前。未尝不善。然虚静之初。亦有清浊之气。此所以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也。未发之前。亦有善恶之几。此所以粹者为善。驳者为恶。人心之未发。即天地之未判也。人心之已发。即天地之已判也。天地未判之前。既有清浊之气。则人心未发之前。岂无善恶之本乎。
五行之禀。在人为五脏。故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而肝肺肾脾各为一物。全塞不通。惟心无对。方寸空虚。五行精英聚焉。故心者气之精爽。盖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者也。故人之五脏。五行之质也。心之神明。五行之气也。(朱子曰惟心无对。又曰心属火。缘是个光明发动底物。所以具得许多道理。)
理本纯善。故性为纯善。气有清浊。故心有善恶。天理纯善。人所同得。气质美恶。人人各殊。然而理坠在气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2L 页
 中。有性之名。则性之本体。不杂乎气。而宲不离乎气。故因其不杂而单指其理。则为本然之性而无不善焉。因其不离而兼指其气。则为气质之性而亦有善恶焉。
中。有性之名。则性之本体。不杂乎气。而宲不离乎气。故因其不杂而单指其理。则为本然之性而无不善焉。因其不离而兼指其气。则为气质之性而亦有善恶焉。虚灵知觉。皆兼体用。虚灵是心之气象也。知觉是心之情状也。心之气象。至虚至灵。不惟未发时为然。已发之后。亦未尝不虚。所谓心兮本虚。应物无迹者是也。心之情状。能知能觉。不惟已发时为然。未发之前。亦未尝无觉。所谓静中有物。只是知觉者是也。然虚灵故知觉。非知觉故虚灵。则虚灵为体。知觉为用。而非虚灵之外。复有知觉也。故朱子曰虚灵知觉。一而已矣。
四端七情。本是一涂。四端衍而为七情。七情约而为四端。初非四端之外。复有七情。七情之外。复有四端也。故四端七情。皆兼善恶。喜怒哀惧之直出横生。恻隐羞恶之中节不中节。莫非兼善恶而言也。
太极之理。赋而为性。阴阳之气。聚而为心。心一阴阳也。形而下之器也。性一太极也。形而上之道也。故邵子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盖心者五气之精爽。一身之主宰也。性者万理之总会。一心之准则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3H 页
 也。其未发也。阴之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其已发也。阳之动也。太极之用所以行也。
也。其未发也。阴之静也。太极之体所以立也。其已发也。阳之动也。太极之用所以行也。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动静者气也。动之静之者理也。故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盖四端七情。皆兼善恶。而气发理乘。只是一涂。理之乘清气而发者。直遂其本然之善。而气听命于理则为善情。理之乘浊气而发者。自汩其本然之善。而理听命于气则为恶情。情之善者。天理主宰而气不能掩蔽也。情之恶者。浊气用事而理不能直遂也。然无论善恶。而能觉者心。所觉者性也。能觉是动处。所觉是动底。故栗谷先生曰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无以发。非理无所发。亦此意尔。(朱子曰七情横贯。四端过了。又曰恻隐也有中节不中节。又曰人之所以为心。不外是四者。)
五行之气在人心者。本不相外而亦不相混合。而为一气分而为五气。故木之神为仁。火之神为礼。而仁外无礼。礼外无仁。金之神为义。水之神为智。而义外无智。智外无义。合为一性。而亦不相外。分为五性。亦不相混。(语类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不相浑故一心之中。五性都具。无有先后。而五性之发。随事迭应。无有次第。不相外故一性之中。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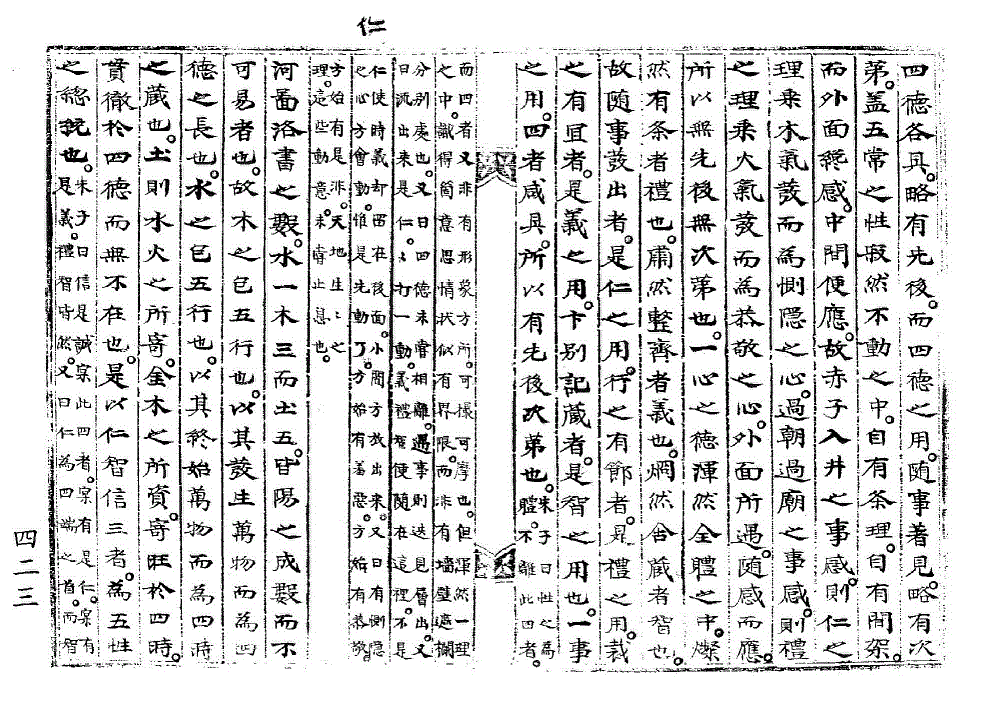 四德各具。略有先后。而四德之用。随事著见。略有次第。盖五常之性寂然不动之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而外面才感。中间便应。故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乘木气发而为恻隐之心。过朝过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乘火气发而为恭敬之心。外面所遇。随感而应。所以无先后无次第也。一心之德浑然全体之中。灿然有条者礼也。肃然整齐者义也。烱然含藏者智也。故随事发出者。是仁之用。行之有节者。是礼之用。裁之有宜者。是义之用。卞别记藏者。是智之用也。一事之用。四者咸具。所以有先后次第也。(朱子曰性之为体。不离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浑然一理之中。识得个意思情状似有界限。而非有墙壁遮栏分别处也。又曰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又曰流出来是仁。仁打一动。义礼智便随在这里。不是仁使时义却留在后面。小间方放出来。又曰有恻隐之心方会动。惟是先动了。方始有羞恶。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天地生生之理。这些动意。未尝止息也。)
四德各具。略有先后。而四德之用。随事著见。略有次第。盖五常之性寂然不动之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而外面才感。中间便应。故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乘木气发而为恻隐之心。过朝过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乘火气发而为恭敬之心。外面所遇。随感而应。所以无先后无次第也。一心之德浑然全体之中。灿然有条者礼也。肃然整齐者义也。烱然含藏者智也。故随事发出者。是仁之用。行之有节者。是礼之用。裁之有宜者。是义之用。卞别记藏者。是智之用也。一事之用。四者咸具。所以有先后次第也。(朱子曰性之为体。不离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浑然一理之中。识得个意思情状似有界限。而非有墙壁遮栏分别处也。又曰四德未尝相离。遇事则迭见层出。又曰流出来是仁。仁打一动。义礼智便随在这里。不是仁使时义却留在后面。小间方放出来。又曰有恻隐之心方会动。惟是先动了。方始有羞恶。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天地生生之理。这些动意。未尝止息也。)河啚洛书之数。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阳之成数而不可易者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发生万物而为四德之长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终始万物而为四时之藏也。土则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资。寄旺于四时。贯彻于四德而无不在也。是以仁智信三者。为五性之总统也。(朱子曰信是诚宲此四者。宲有是仁。宲有是义。礼智皆然。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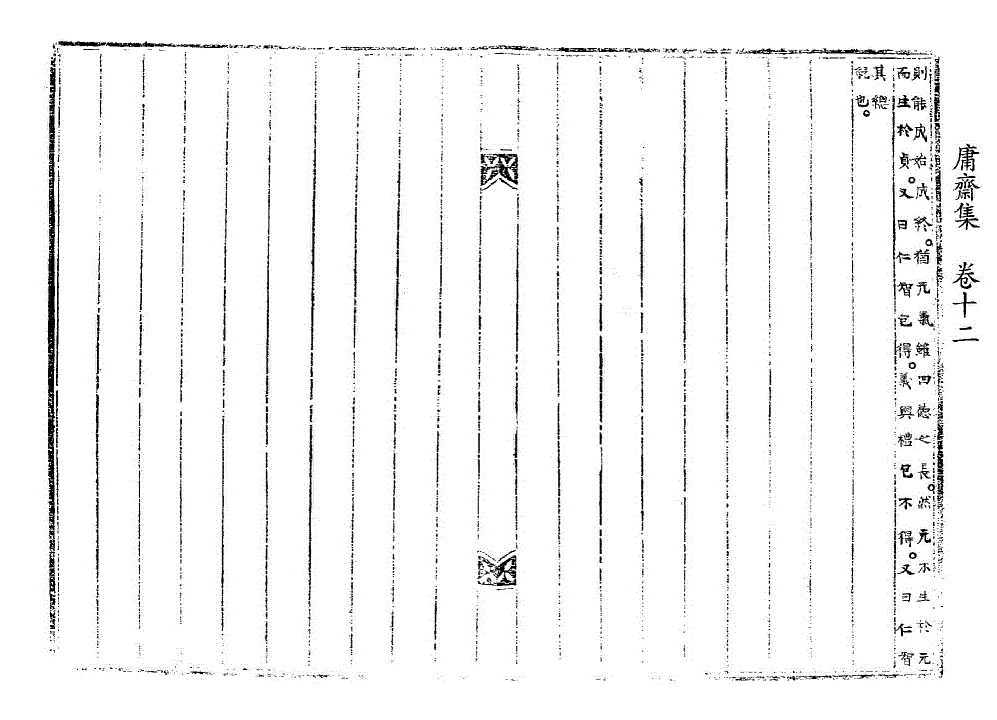 则能成始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又曰仁智包得。义与礼包不得。又曰仁智其总统也。)
则能成始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又曰仁智包得。义与礼包不得。又曰仁智其总统也。)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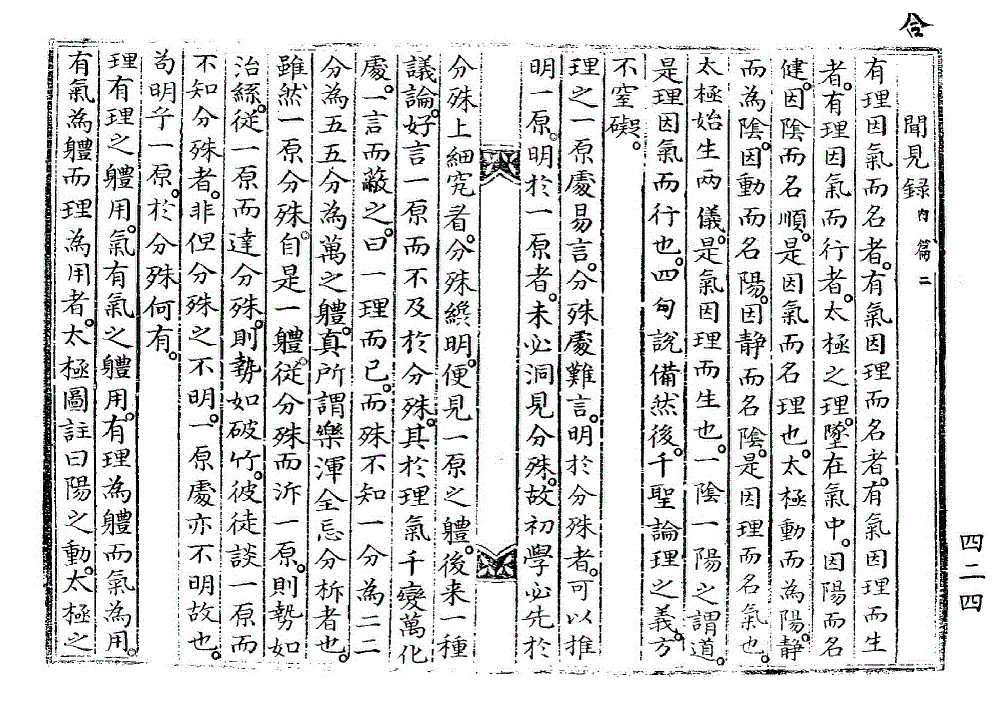 闻见录(内篇二)주-D001
闻见录(内篇二)주-D001有理因气而名者。有气因理而名者。有气因理而生者。有理因气而行者。太极之理。坠在气中。因阳而名健。因阴而名顺。是因气而名理也。太极动而为阳。静而为阴。因动而名阳。因静而名阴。是因理而名气也。太极始生两仪。是气因理而生也。一阴一阳之谓道。是理因气而行也。四句说备然后。千圣论理之义。方不窒碍。
理之一原处易言。分殊处难言。明于分殊者。可以推明一原。明于一原者。未必洞见分殊。故初学必先于分殊上细究看。分殊才明。便见一原之体。后来一种议论。好言一原而不及于分殊。其于理气千变万化处。一言而蔽之。曰一理而已。而殊不知一分为二二分为五五分为万之体。真所谓乐浑全忘分析者也。虽然一原分殊。自是一体。从分殊而溯一原。则势如治丝。从一原而达分殊。则势如破竹。彼徒谈一原而不知分殊者。非但分殊之不明。一原处亦不明故也。苟明乎一原。于分殊何有。
理有理之体用。气有气之体用。有理为体而气为用。有气为体而理为用者。太极图注曰阳之动。太极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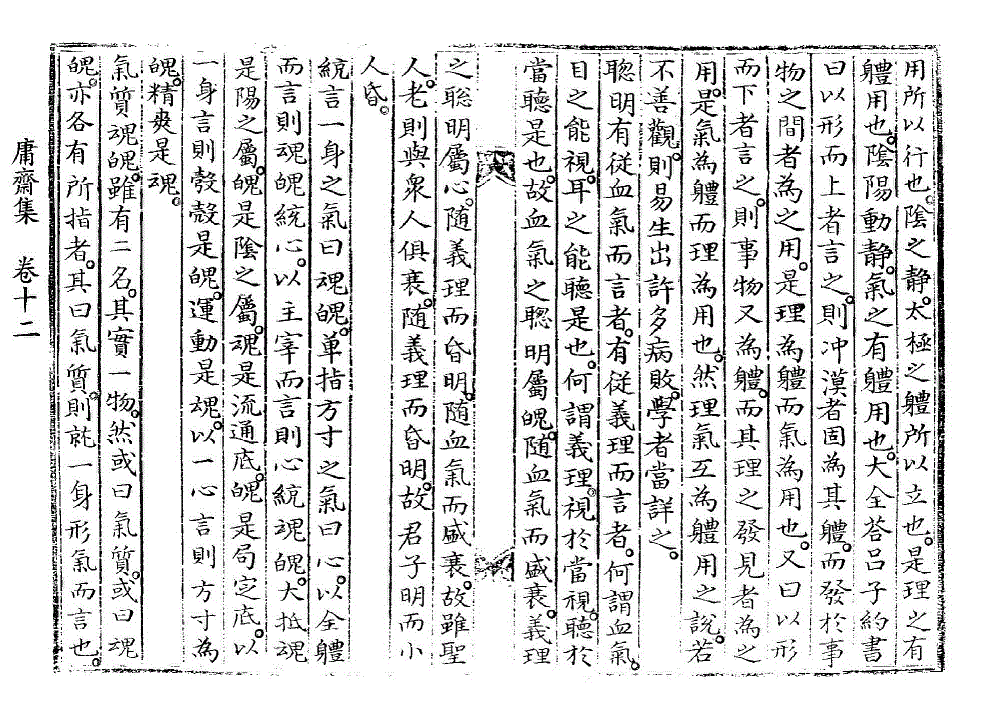 用所以行也。阴之静。太极之体所以立也。是理之有体用也。阴阳动静。气之有体用也。大全答吕子约书曰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其体。而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是理为体而气为用也。又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是气为体而理为用也。然理气互为体用之说。若不善观。则易生出许多病败。学者当详之。
用所以行也。阴之静。太极之体所以立也。是理之有体用也。阴阳动静。气之有体用也。大全答吕子约书曰以形而上者言之。则冲漠者固为其体。而发于事物之间者为之用。是理为体而气为用也。又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则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是气为体而理为用也。然理气互为体用之说。若不善观。则易生出许多病败。学者当详之。聪明有从血气而言者。有从义理而言者。何谓血气。目之能视。耳之能听是也。何谓义理。视于当视。听于当听是也。故血气之聪明属魄。随血气而盛衰。义理之聪明属心。随义理而昏明。随血气而盛衰。故虽圣人。老则与众人俱衰。随义理而昏明。故君子明而小人昏。
统言一身之气曰魂魄。单指方寸之气曰心。以全体而言则魂魄统心。以主宰而言则心统魂魄。大抵魂是阳之属。魄是阴之属。魂是流通底。魄是局定底。以一身言则彀壳是魄。运动是魂。以一心言则方寸为魄。精爽是魂。
气质魂魄。虽有二名。其实一物。然或曰气质。或曰魂魄。亦各有所指者。其曰气质。则就一身形气而言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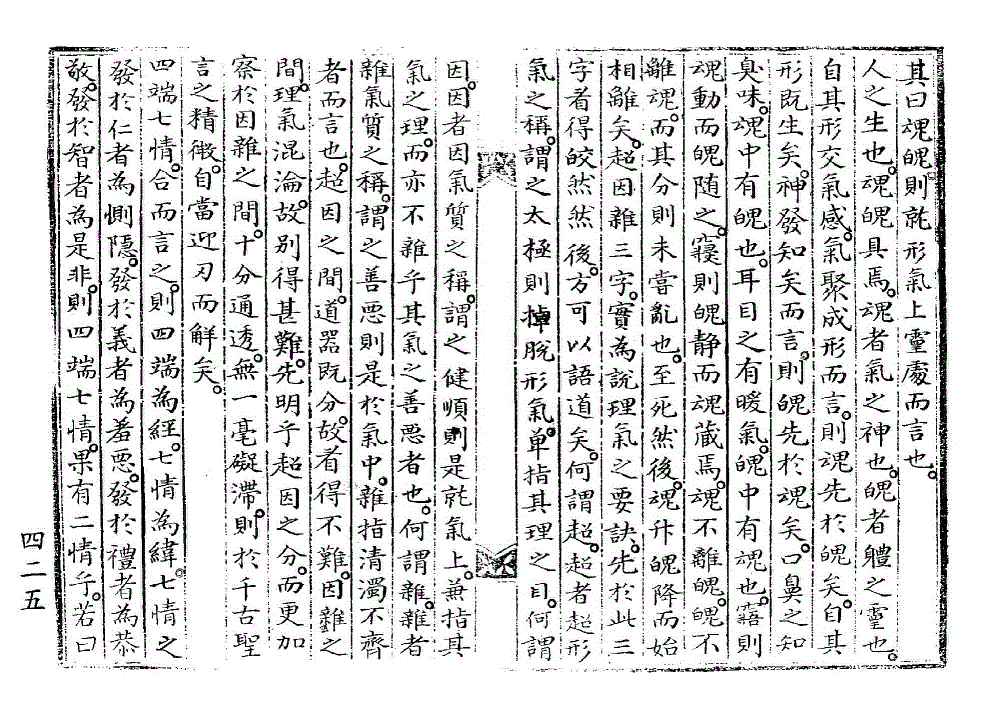 其曰魂魄。则就形气上灵处而言也。
其曰魂魄。则就形气上灵处而言也。人之生也。魂魄具焉。魂者气之神也。魄者体之灵也。自其形交气感。气聚成形而言。则魂先于魄矣。自其形既生矣。神发知矣而言。则魄先于魂矣。口鼻之知臭味。魂中有魄也。耳目之有暖气。魄中有魂也。寤则魂动而魄随之。寝则魄静而魂藏焉。魂不离魄。魄不离魂。而其分则未尝乱也。至死然后。魂升魄降而始相离矣。超因杂三字。实为说理气之要诀。先于此三字看得皎然然后。方可以语道矣。何谓超。超者超形气之称。谓之太极则掉脱形气。单指其理之目。何谓因。因者因气质之称。谓之健顺则是就气上。兼指其气之理。而亦不杂乎其气之善恶者也。何谓杂。杂者杂气质之称。谓之善恶则是于气中。杂指清浊不齐者而言也。超因之间。道器既分。故看得不难。因杂之间。理气混沦。故别得甚难。先明乎超因之分。而更加察于因杂之间。十分通透。无一毫碍滞。则于千古圣言之精微。自当迎刃而解矣。
四端七情。合而言之。则四端为经。七情为纬。七情之发于仁者为恻隐。发于义者为羞恶。发于礼者为恭敬。发于智者为是非。则四端七情。果有二情乎。若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6H 页
 七情发于仁而有不为恻隐者。发于义而有不为羞恶者。发于礼发于智而有不为恭敬是非者。则是性之用。别行于四端之外。而四端亦不足以尽人心之用矣。岂理也哉。
七情发于仁而有不为恻隐者。发于义而有不为羞恶者。发于礼发于智而有不为恭敬是非者。则是性之用。别行于四端之外。而四端亦不足以尽人心之用矣。岂理也哉。五气之精爽。聚而为虚灵。因虚灵而有知觉。则虚灵知觉。原非二物。然谓之虚灵之理。则当统称五性。谓之知觉之理。则当偏属智一边矣。
心纯善之说。实是前古所未闻。而其为吾道之害。实无穷。圣贤千言万语。学者吃紧工夫。都在此一心上。此心果为纯善。则纯善之上。不必下他工夫。大学之诚意正心。中庸之存养省察。莫是其虚事耶。
栗谷与牛溪书。有曰理与气何处见其异。又曰何处见理自理气自气。此二说。高山丈以为栗翁之意。欲闻一而二之问。恐未然。牛溪之见。每以理气分为二物。栗谷所争。每在二而一之上。若如高山说。则一而二之分。牛溪之所已洞见处。不必执此为问矣。
医书以七情分属五脏。而七情有伤。治其所属之脏则尽有效。非七情分出于诸脏也。七情皆发于心。而心用七情。乃或系于诸脏矣。此即是五行生克制化之理也。医书曰肺在志为悲。又曰心虚则悲。曰肾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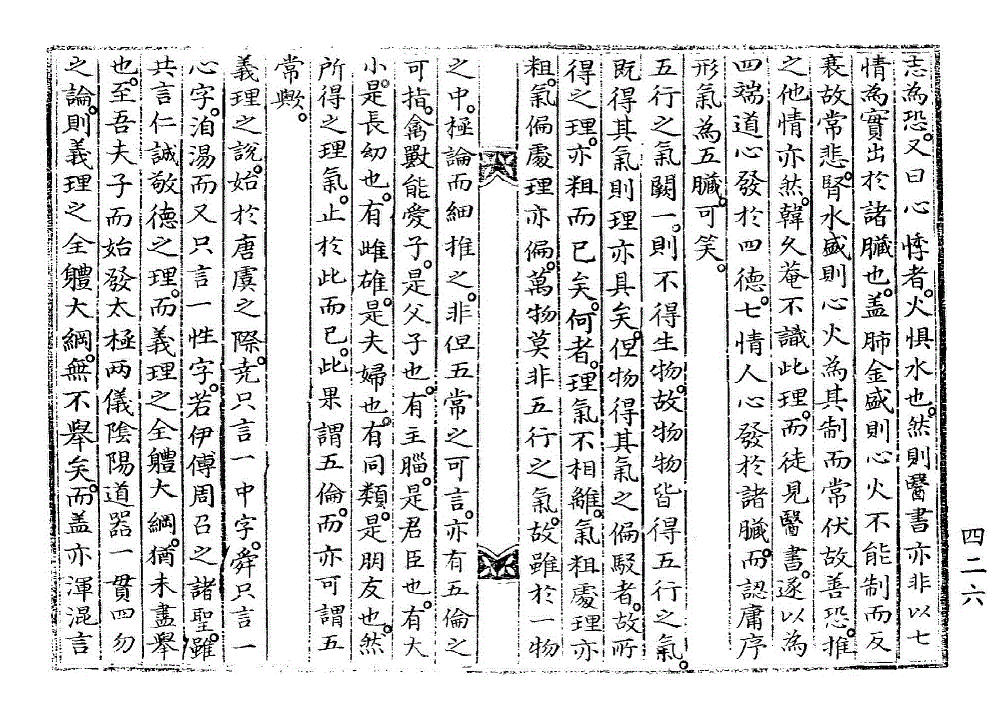 志为恐。又曰心悸者。火惧水也。然则医书亦非以七情为实出于诸脏也。盖肺金盛则心火不能制而反衰故常悲。肾水盛则心火为其制而常伏故善恐。推之他情亦然。韩久庵不识此理。而徒见医书。遂以为四端道心发于四德。七情人心发于诸脏。而认庸序形气为五脏。可笑。
志为恐。又曰心悸者。火惧水也。然则医书亦非以七情为实出于诸脏也。盖肺金盛则心火不能制而反衰故常悲。肾水盛则心火为其制而常伏故善恐。推之他情亦然。韩久庵不识此理。而徒见医书。遂以为四端道心发于四德。七情人心发于诸脏。而认庸序形气为五脏。可笑。五行之气阙一。则不得生物。故物物皆得五行之气。既得其气则理亦具矣。但物得其气之偏驳者。故所得之理。亦粗而已矣。何者。理气不相离。气粗处理亦粗。气偏处理亦偏。万物莫非五行之气。故虽于一物之中。极论而细推之。非但五常之可言。亦有五伦之可指。禽兽能爱子。是父子也。有主脑。是君臣也。有大小。是长幼也。有雌雄。是夫妇也。有同类。是朋友也。然所得之理气。止于此而已。此果谓五伦。而亦可谓五常欤。
义理之说。始于唐虞之际。尧只言一中字。舜只言一心字。洎汤而又只言一性字。若伊傅周召之诸圣。虽共言仁诚敬德之理。而义理之全体大纲。犹未尽举也。至吾夫子而始发太极两仪阴阳道器一贯四勿之论。则义理之全体大纲。无不举矣。而盖亦浑混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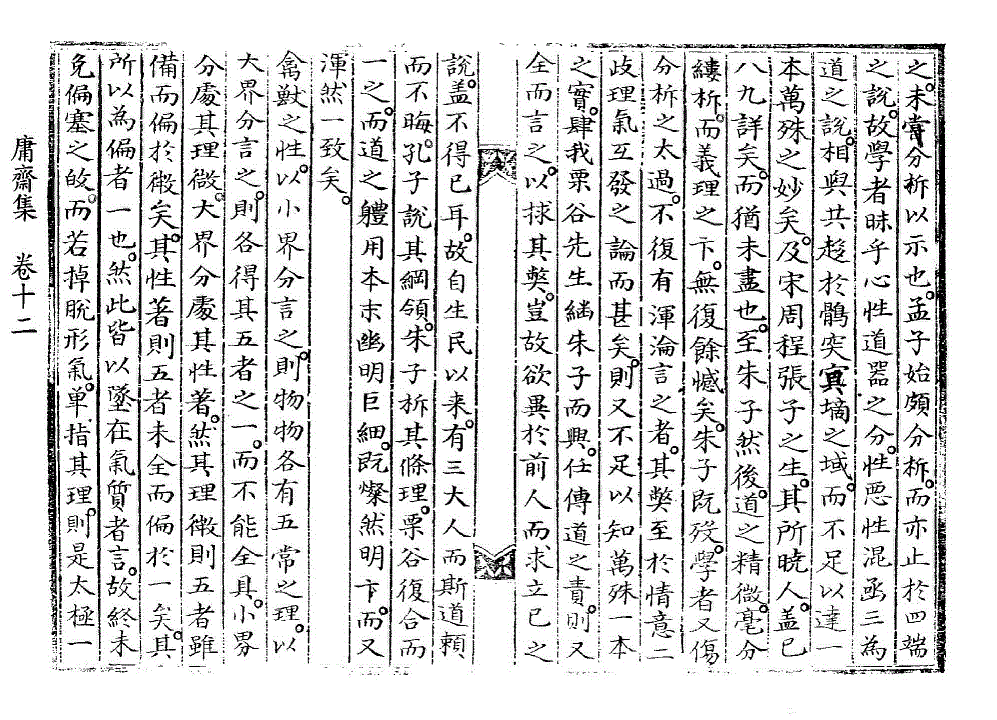 之。未尝分析以示也。孟子始颇分析。而亦止于四端之说。故学者昧乎心性道器之分。性恶性混函三为道之说。相与共趍于鹘突冥墑之域。而不足以达一本万殊之妙矣。及宋周程张子之生。其所晓人。盖已八九详矣。而犹未尽也。至朱子然后。道之精微。毫分缕析。而义理之卞。无复馀憾矣。朱子既殁。学者又伤分析之太过。不复有浑沦言之者。其弊至于情意二歧理气互发之论而甚矣。则又不足以知万殊一本之实。肆我栗谷先生继朱子而兴。任传道之责。则又全而言之。以救其弊。岂故欲异于前人而求立己之说。盖不得已耳。故自生民以来。有三大人而斯道赖而不晦。孔子说其纲领。朱子析其条理。栗谷复合而一之。而道之体用本末幽明巨细。既灿然明卞。而又浑然一致矣。
之。未尝分析以示也。孟子始颇分析。而亦止于四端之说。故学者昧乎心性道器之分。性恶性混函三为道之说。相与共趍于鹘突冥墑之域。而不足以达一本万殊之妙矣。及宋周程张子之生。其所晓人。盖已八九详矣。而犹未尽也。至朱子然后。道之精微。毫分缕析。而义理之卞。无复馀憾矣。朱子既殁。学者又伤分析之太过。不复有浑沦言之者。其弊至于情意二歧理气互发之论而甚矣。则又不足以知万殊一本之实。肆我栗谷先生继朱子而兴。任传道之责。则又全而言之。以救其弊。岂故欲异于前人而求立己之说。盖不得已耳。故自生民以来。有三大人而斯道赖而不晦。孔子说其纲领。朱子析其条理。栗谷复合而一之。而道之体用本末幽明巨细。既灿然明卞。而又浑然一致矣。禽兽之性。以小界分言之。则物物各有五常之理。以大界分言之。则各得其五者之一。而不能全具。小界分处其理微。大界分处其性著。然其理微则五者虽备而偏于微矣。其性著则五者未全而偏于一矣。其所以为偏者一也。然此皆以坠在气质者言。故终未免偏塞之敀。而若掉脱形气。单指其理。则是太极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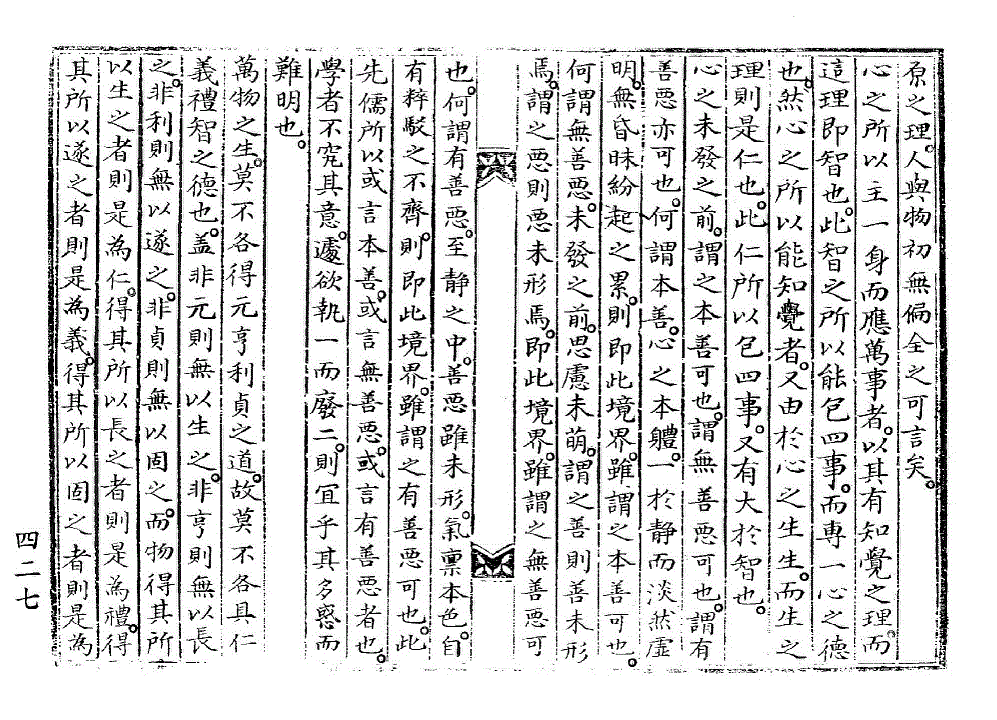 原之理。人与物初无偏全之可言矣。
原之理。人与物初无偏全之可言矣。心之所以主一身而应万事者。以其有知觉之理。而这理即智也。此智之所以能包四事。而专一心之德也。然心之所以能知觉者。又由于心之生生。而生之理则是仁也。此仁所以包四事。又有大于智也。
心之未发之前。谓之本善可也。谓无善恶可也。谓有善恶亦可也。何谓本善。心之本体。一于静而淡然虚明。无昏昧纷起之累。则即此境界。虽谓之本善可也。何谓无善恶。未发之前。思虑未萌。谓之善则善未形焉。谓之恶则恶未形焉。即此境界。虽谓之无善恶可也。何谓有善恶。至静之中。善恶虽未形。气禀本色。自有粹驳之不齐。则即此境界。虽谓之有善恶可也。此先儒所以或言本善。或言无善恶。或言有善恶者也。学者不究其意。遽欲执一而废二。则宜乎其多惑而难明也。
万物之生。莫不各得元亨利贞之道。故莫不各具仁义礼智之德也。盖非元则无以生之。非亨则无以长之。非利则无以遂之。非贞则无以固之。而物得其所以生之者则是为仁。得其所以长之者则是为礼。得其所以遂之者则是为义。得其所以固之者则是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H 页
 智。然天之所以生之长之遂之固之者。必因是气而遂之。而其气有偏正。故其理亦随而偏正。此人物之性。所以终不同也。
智。然天之所以生之长之遂之固之者。必因是气而遂之。而其气有偏正。故其理亦随而偏正。此人物之性。所以终不同也。古人制服之义。自有大经。先明乎大经。则其馀自当推去。其法有三(一作二)。一曰四道。二曰三属。何谓四道。推父道至于从父。推母道至于从母。推己道至于从兄弟及姊妹。推子道至于从侄。至于兄弟之妻。则当推妻道。而推妻道有嫌。故古礼嫂叔则无服。何谓三属。父之属有九。自高祖至玄孙为九。母之属有三。自祖至兄弟为三。妻之属有一。妻之父母是也。古服之制。盖出于此。故各有条理。易得领会。而后来从厚加服。故其制错杂。卒难领会。终不若古义之昭然不紊矣。
或以圣与神。分作两等境界。圣上谓有神人。而以尧舜为神。神下谓有圣人。而以孔子为圣。其说甚误。神与圣。比若无极而太极。圣上别无神。而神外别无圣矣。神圣岂有两般经界。尧舜孔子本一神圣。而有为无为。各自不同。故后人错以为圣上真有神域。而其实时使之然也。尧舜之世。淳元未散。不言而信。无为而化。此五帝所以垂拱而治也。至于夫子之时。世道日下。利欲纷挐。邪说横流。夫子不得不极论昭说。丕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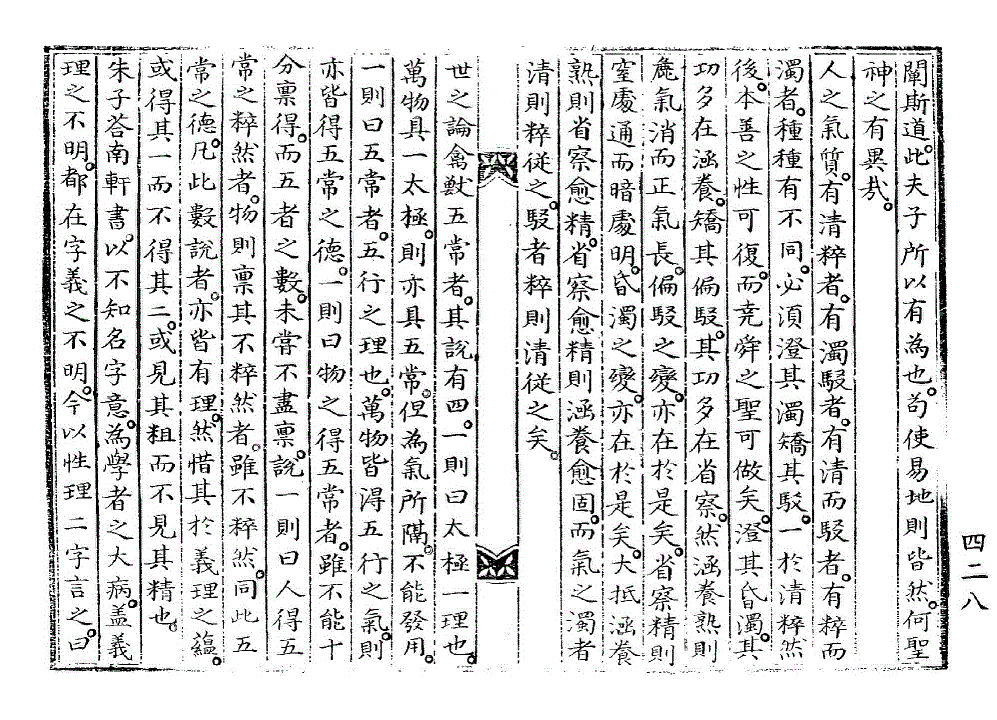 阐斯道。此夫子所以有为也。苟使易地则皆然。何圣神之有异哉。
阐斯道。此夫子所以有为也。苟使易地则皆然。何圣神之有异哉。人之气质。有清粹者。有浊驳者。有清而驳者。有粹而浊者。种种有不同。必须澄其浊矫其驳。一于清粹然后。本善之性可复。而尧舜之圣可做矣。澄其昏浊。其功多在涵养。矫其偏驳。其功多在省察。然涵养熟则粗气消而正气长。偏驳之变。亦在于是矣。省察精则窒处通而暗处明。昏浊之变。亦在于是矣。大抵涵养熟则省察愈精。省察愈精则涵养愈固。而气之浊者清则粹从之。驳者粹则清从之矣。
世之论禽兽五常者。其说有四。一则曰太极一理也。万物具一太极。则亦具五常。但为气所隔。不能发用。一则曰五常者。五行之理也。万物皆得五行之气。则亦皆得五常之德。一则曰物之得五常者。虽不能十分禀得。而五者之数。未尝不尽禀。说一则曰人得五常之粹然者。物则禀其不粹然者。虽不粹然。同此五常之德。凡此数说者。亦皆有理。然惜其于义理之蕴。或得其一而不得其二。或见其粗而不见其精也。
朱子答南轩书。以不知名字意。为学者之大病。盖义理之不明。都在字义之不明。今以性理二字言之。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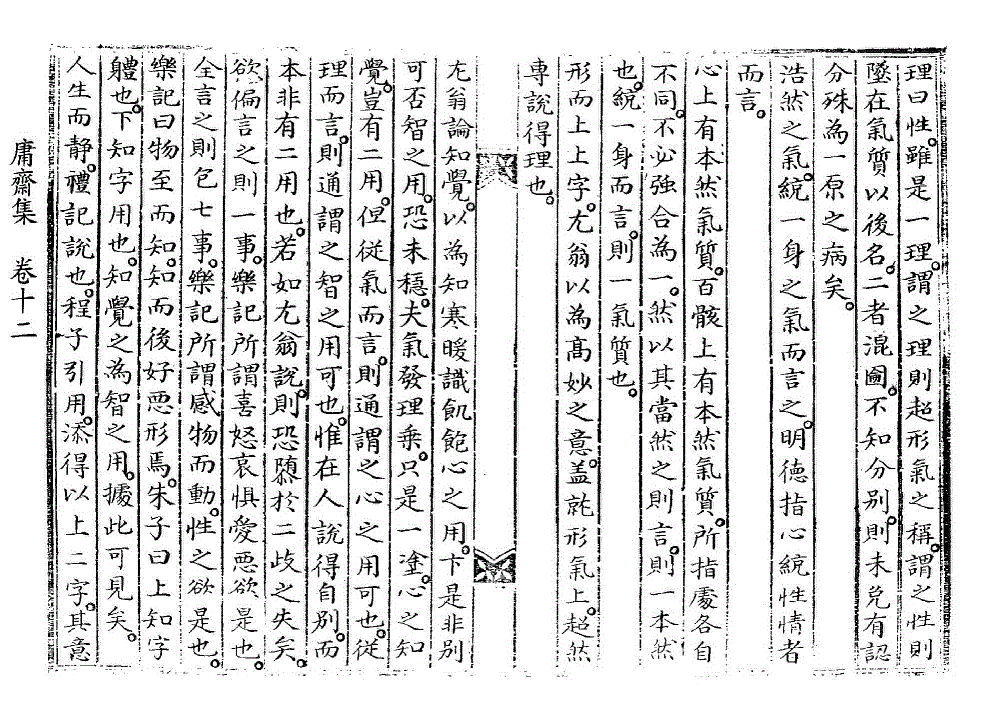 理曰性。虽是一理。谓之理则超形气之称。谓之性则坠在气质以后名。二者混囵。不知分别。则未免有认分殊为一原之病矣。
理曰性。虽是一理。谓之理则超形气之称。谓之性则坠在气质以后名。二者混囵。不知分别。则未免有认分殊为一原之病矣。浩然之气。统一身之气而言之。明德指心统性情者而言。
心上有本然气质。百骸上有本然气质。所指处各自不同。不必强合为一。然以其当然之则言。则一本然也。统一身而言。则一气质也。
形而上上字。尤翁以为高妙之意。盖就形气上。超然专说得理也。
尤翁论知觉。以为知寒暖识饥饱心之用。卞是非别可否智之用。恐未稳。夫气发理乘。只是一涂。心之知觉。岂有二用。但从气而言。则通谓之心之用可也。从理而言。则通谓之智之用可也。惟在人说得自别。而本非有二用也。若如尤翁说。则恐隳于二歧之失矣。欲偏言之则一事。乐记所谓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也。全言之则包七事。乐记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是也。乐记曰物至而知。知而后好恶形焉。朱子曰上知字体也。下知字用也。知觉之为智之用。据此可见矣。
人生而静。礼记说也。程子引用。添得以上二字。其意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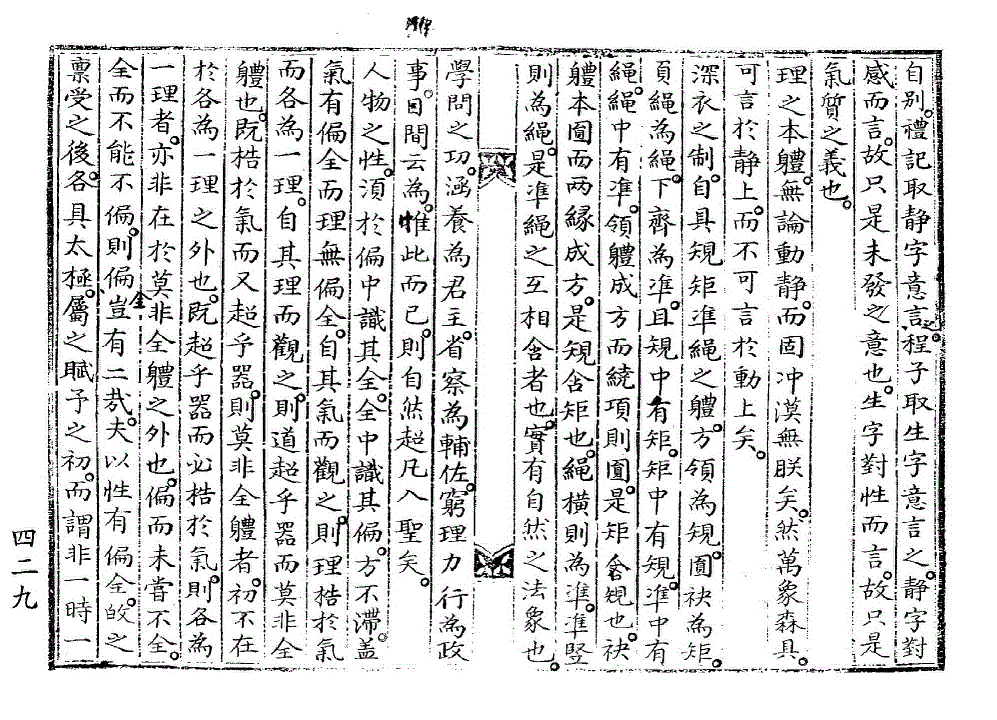 自别。礼记取静字意言之。程子取生字意言之。静字对感而言。故只是未发之意也。生字对性而言。故只是气质之义也。
自别。礼记取静字意言之。程子取生字意言之。静字对感而言。故只是未发之意也。生字对性而言。故只是气质之义也。理之本体。无论动静。而固冲漠无眹矣。然万象森具。可言于静上。而不可言于动上矣。
深衣之制。自具规矩准绳之体。方领为规。圆袂为矩。负绳为绳。下齐为准。且规中有矩。矩中有规。准中有绳。绳中有准。领体成方而绕项则圆。是矩含规也。袂体本圆而两缘成方。是规含矩也。绳横则为准。准竖则为绳。是准绳之互相含者也。实有自然之法象也。学问之功。涵养为君主。省察为辅佐。穷理力行为政事。日间云为。惟此而已。则自然超凡入圣矣。
人物之性。须于偏中识其全。全中识其偏。方不滞。盖气有偏全而理无偏全。自其气而观之。则理梏于气而各为一理。自其理而观之。则道超乎器而莫非全体也。既梏于气而又超乎器。则莫非全体者。初不在于各为一理之外也。既超乎器而必梏于气。则各为一理者。亦非在于莫非全体之外也。偏而未尝不全。全而不能不偏。则偏全岂有二哉。夫以性有偏全。敀之禀受之后。各具太极。属之赋予之初。而谓非一时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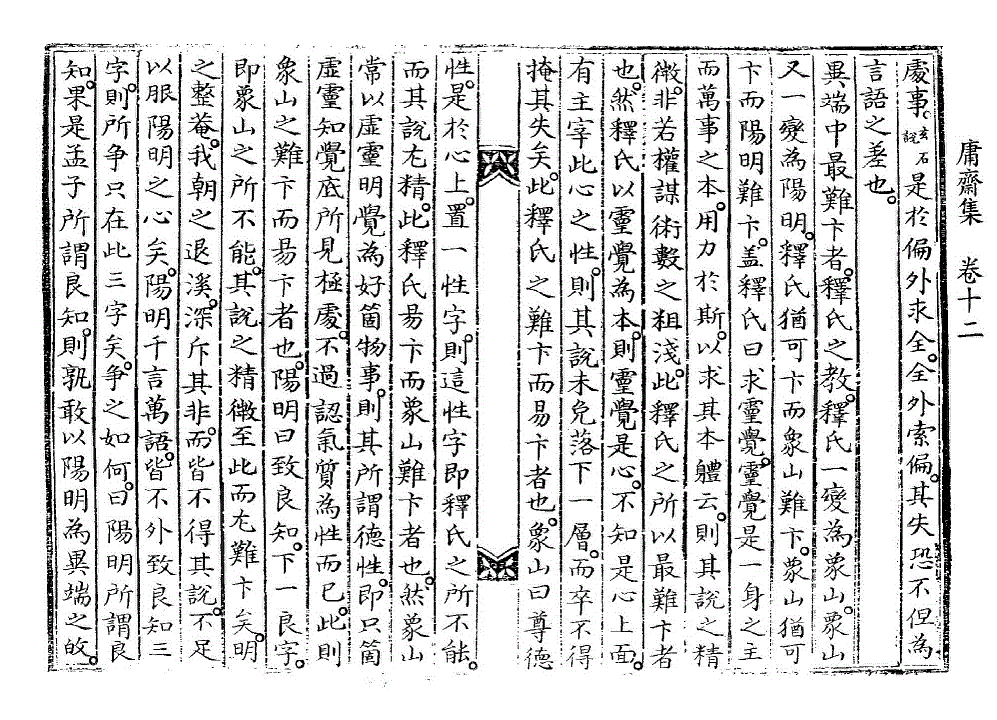 处事。(玄石说)是于偏外求全。全外索偏。其失恐不但为言语之差也。
处事。(玄石说)是于偏外求全。全外索偏。其失恐不但为言语之差也。异端中最难卞者。释氏之教。释氏一变为象山。象山又一变为阳明。释氏犹可卞而象山难卞。象山犹可卞而阳明难卞。盖释氏曰求灵觉。灵觉是一身之主而万事之本。用力于斯。以求其本体云。则其说之精微。非若权谋𧗱数之粗浅。此释氏之所以最难卞者也。然释氏以灵觉为本。则灵觉是心。不知是心上面。有主宰此心之性。则其说未免落下一层。而卒不得掩其失矣。此释氏之难卞而易卞者也。象山曰尊德性。是于心上。置一性字。则这性字即释氏之所不能。而其说尤精。此释氏易卞而象山难卞者也。然象山常以虚灵明觉为好个物事。则其所谓德性。即只个虚灵知觉底所见极处。不过认气质为性而已。此则象山之难卞而易卞者也。阳明曰致良知。下一良字。即象山之所不能。其说之精微至此而尤难卞矣。明之整庵。我朝之退溪。深斥其非。而皆不得其说。不足以服阳明之心矣。阳明千言万语。皆不外致良知三字。则所争只在此三字矣。争之如何。曰阳明所谓良知。果是孟子所谓良知。则孰敢以阳明为异端之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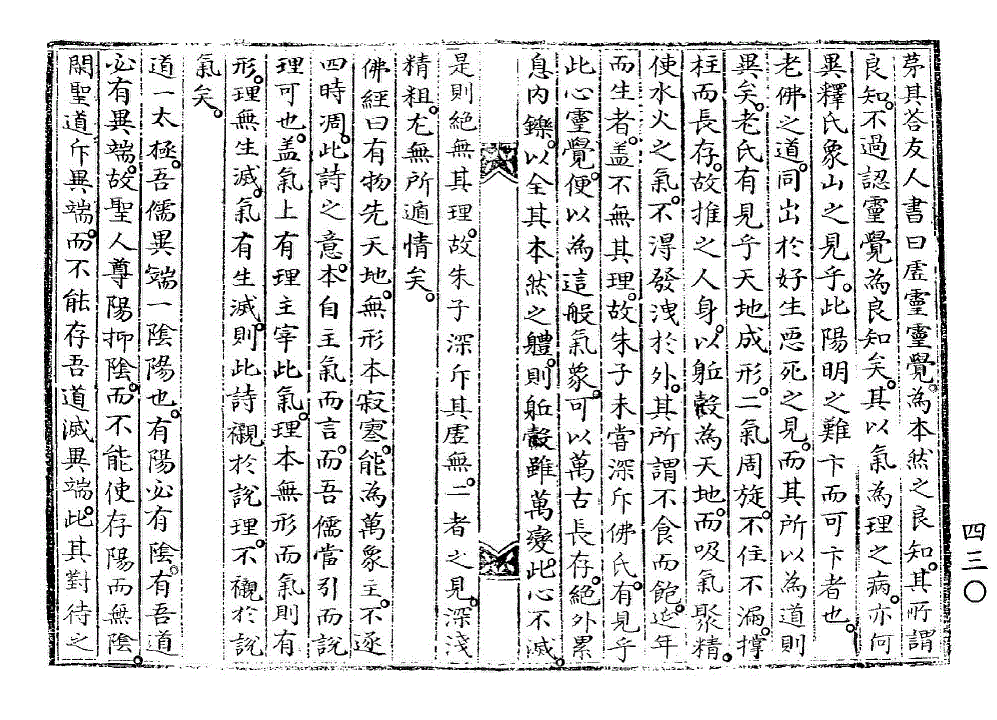 第其答友人书曰虚灵灵觉。为本然之良知。其所谓良知。不过认灵觉为良知矣。其以气为理之病。亦何异释氏象山之见乎。此阳明之难卞而可卞者也。老佛之道。同出于好生恶死之见。而其所以为道则异矣。老氏有见乎天地成形。二气周旋。不住不漏。撑柱而长存。故推之人身。以𨈬壳为天地。而吸气聚精。使水火之气。不得发泄于外。其所谓不食而饱。延年而生者。盖不无其理。故朱子未尝深斥佛氏。有见乎此心灵觉。便以为这般气象。可以万古长存。绝外累息内铄。以全其本然之体。则𨈬壳虽万变。此心不灭。是则绝无其理。故朱子深斥其虚无。二者之见。深浅精粗。尤无所遁情矣。
第其答友人书曰虚灵灵觉。为本然之良知。其所谓良知。不过认灵觉为良知矣。其以气为理之病。亦何异释氏象山之见乎。此阳明之难卞而可卞者也。老佛之道。同出于好生恶死之见。而其所以为道则异矣。老氏有见乎天地成形。二气周旋。不住不漏。撑柱而长存。故推之人身。以𨈬壳为天地。而吸气聚精。使水火之气。不得发泄于外。其所谓不食而饱。延年而生者。盖不无其理。故朱子未尝深斥佛氏。有见乎此心灵觉。便以为这般气象。可以万古长存。绝外累息内铄。以全其本然之体。则𨈬壳虽万变。此心不灭。是则绝无其理。故朱子深斥其虚无。二者之见。深浅精粗。尤无所遁情矣。佛经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此诗之意。本自主气而言。而吾儒当引而说理可也。盖气上有理主宰此气。理本无形而气则有形。理无生灭。气有生灭。则此诗衬于说理。不衬于说气矣。
道一太极。吾儒异端一阴阳也。有阳必有阴。有吾道必有异端。故圣人尊阳抑阴。而不能使存阳而无阴。闲圣道斥异端。而不能存吾道灭异端。此其对待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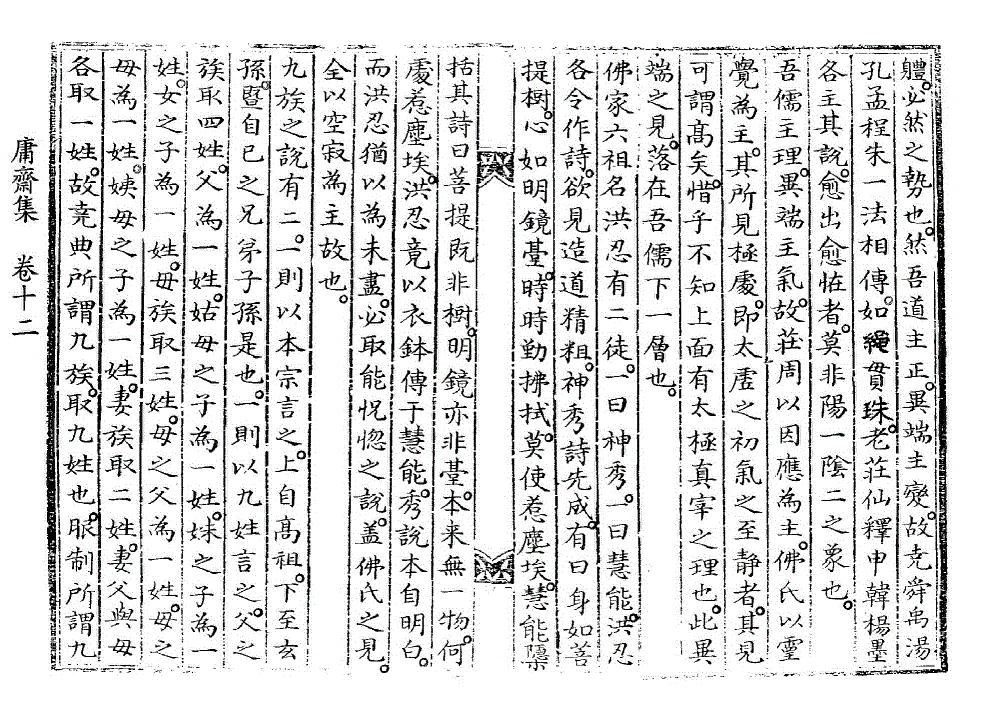 体。必然之势也。然吾道主正。异端主变。故尧舜禹汤孔孟程朱一法相传。如绳贯珠。老庄仙释申韩杨墨各主其说。愈出愈怪者。莫非阳一阴二之象也。
体。必然之势也。然吾道主正。异端主变。故尧舜禹汤孔孟程朱一法相传。如绳贯珠。老庄仙释申韩杨墨各主其说。愈出愈怪者。莫非阳一阴二之象也。吾儒主理。异端主气。故庄周以因应为主。佛氏以灵觉为主。其所见极处。即太虚之初气之至静者。其见可谓高矣。惜乎不知上面有太极真宰之理也。此异端之见。落在吾儒下一层也。
佛家六祖名洪忍有二徒。一曰神秀。一曰慧能。洪忍各令作诗。欲见造道精粗。神秀诗先成。有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檃括其诗曰菩提既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洪忍竟以衣钵传于慧能。秀说本自明白。而洪忍犹以为未尽。必取能恍惚之说。盖佛氏之见。全以空寂为主故也。
九族之说有二。一则以本宗言之。上自高祖。下至玄孙。暨自己之兄弟子孙是也。一则以九姓言之。父之族取四姓。父为一姓。姑母之子为一姓。妹之子为一姓。女之子为一姓。母族取三姓。母之父为一姓。母之母为一姓。姨母之子为一姓。妻族取二姓。妻父与母各取一姓。故尧典所谓九族。取九姓也。服制所谓九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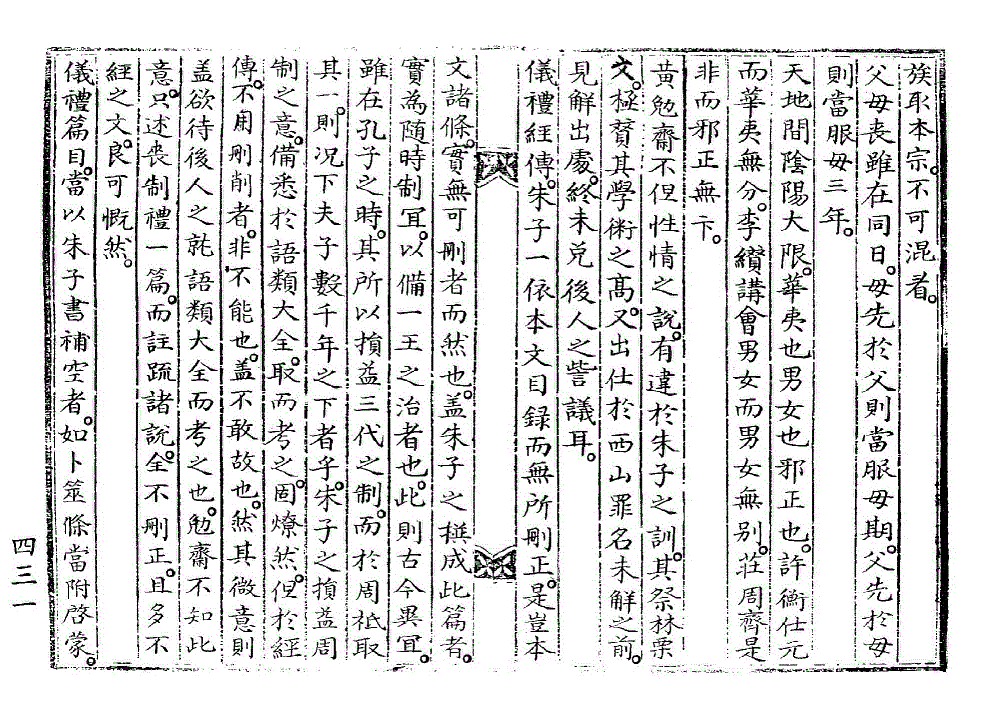 族取本宗。不可混看。
族取本宗。不可混看。父母丧虽在同日。母先于父则当服母期。父先于母则当服母三年。
天地间阴阳大限。华夷也男女也邪正也。许衡仕元而华夷无分。李缵讲会男女而男女无别。庄周齐是非而邪正无卞。
黄勉斋不但性情之说。有违于朱子之训。其祭林栗文。极赞其学𧗱之高。又出仕于西山罪名未解之前。见解出处。终未免后人之訾议耳。
仪礼经传。朱子一依本文目录而无所删正。是岂本文诸条。实无可删者而然也。盖朱子之撰成此篇者。实为随时制宜。以备一王之治者也。此则古今异宜。虽在孔子之时。其所以损益三代之制。而于周祗取其一。则况下夫子数千年之下者乎。朱子之损益周制之意。备悉于语类大全。取而考之。固燎然。但于经传。不用删削者。非不能也。盖不敢故也。然其微意则盖欲待后人之就语类大全而考之也。勉斋不知此意。只述丧制礼一篇。而注疏诸说。全不删正。且多不经之文。良可慨然。
仪礼篇目。当以朱子书补空者。如卜筮条当附启蒙。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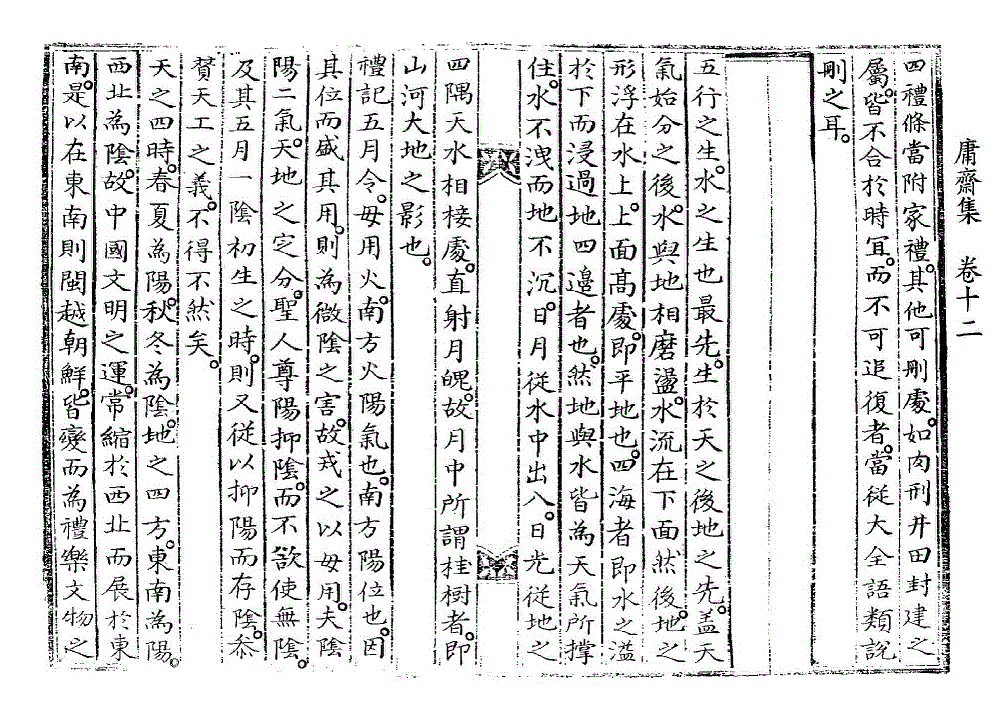 四礼条当附家礼。其他可删处。如肉刑井田封建之属。皆不合于时宜。而不可追复者。当从大全语类说删之耳。
四礼条当附家礼。其他可删处。如肉刑井田封建之属。皆不合于时宜。而不可追复者。当从大全语类说删之耳。五行之生。水之生也最先。生于天之后地之先。盖天气始分之后。水与地相磨荡。水流在下面然后。地之形浮在水上。上面高处。即平地也。四海者即水之溢于下而浸过地四边者也。然地与水皆为天气所撑住。水不泄而地不沉。日月从水中出入。日光从地之四隅天水相椄处。直射月魄。故月中所谓桂树者。即山河大地之影也。
礼记五月令。毋用火。南方火阳气也。南方阳位也。因其位而盛其用。则为微阴之害。故戒之以毋用。夫阴阳二气。天地之定分。圣人尊阳抑阴。而不欲使无阴。及其五月一阴初生之时。则又从以抑阳而存阴。参赞天工之义。不得不然矣。
天之四时。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地之四方。东南为阳。西北为阴。故中国文明之运。常缩于西北而展于东南。是以在东南则闽越朝鲜。皆变而为礼乐文物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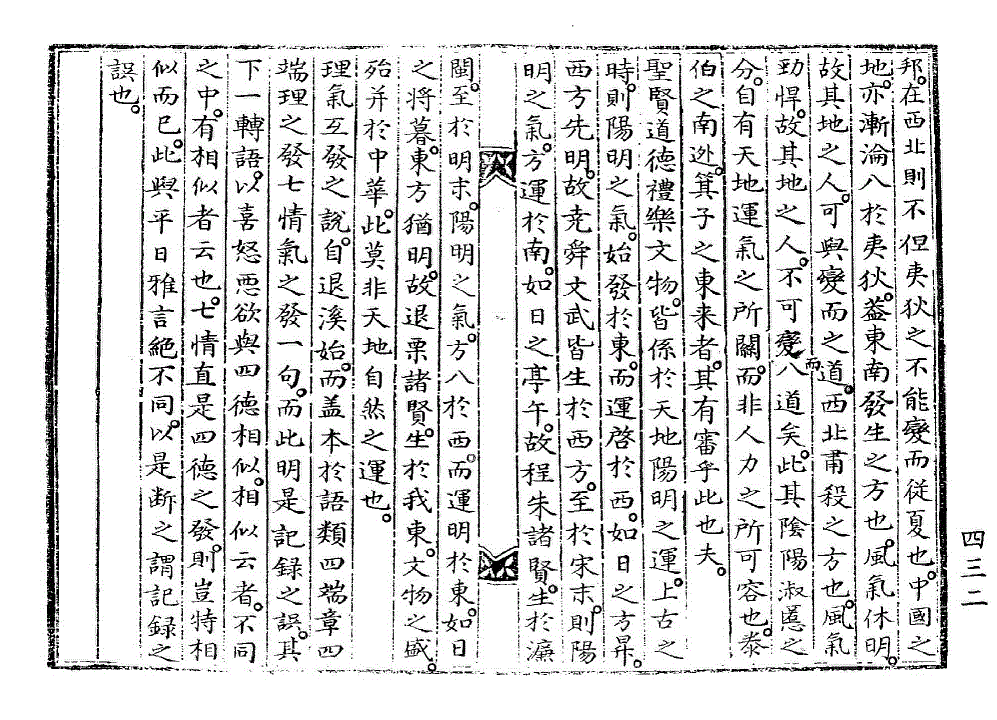 邦。在西北则不但夷狄之不能变而从夏也。中国之地。亦渐沦入于夷狄。盖东南发生之方也。风气休明。故其地之人。可与变而之道。西北肃杀之方也。风气劲悍。故其地之人。不可变而入道矣。此其阴阳淑慝之分。自有天地运气之所关。而非人力之所可容也。泰伯之南逃。箕子之东来者。其有审乎此也夫。
邦。在西北则不但夷狄之不能变而从夏也。中国之地。亦渐沦入于夷狄。盖东南发生之方也。风气休明。故其地之人。可与变而之道。西北肃杀之方也。风气劲悍。故其地之人。不可变而入道矣。此其阴阳淑慝之分。自有天地运气之所关。而非人力之所可容也。泰伯之南逃。箕子之东来者。其有审乎此也夫。圣贤道德礼乐文物。皆系于天地阳明之运。上古之时。则阳明之气。始发于东。而运启于西。如日之方升。西方先明。故尧舜文武皆生于西方。至于宋末。则阳明之气。方运于南。如日之亭午。故程朱诸贤。生于濂闽。至于明末。阳明之气。方入于西。而运明于东。如日之将暮。东方犹明。故退栗诸贤。生于我东。文物之盛。殆并于中华。此莫非天地自然之运也。
理气互发之说。自退溪始。而盖本于语类四端章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一句。而此明是记录之误。其下一转语。以喜怒恶欲与四德相似。相似云者。不同之中。有相似者云也。七情直是四德之发。则岂特相似而已。此与平日雅言绝不同。以是断之谓记录之误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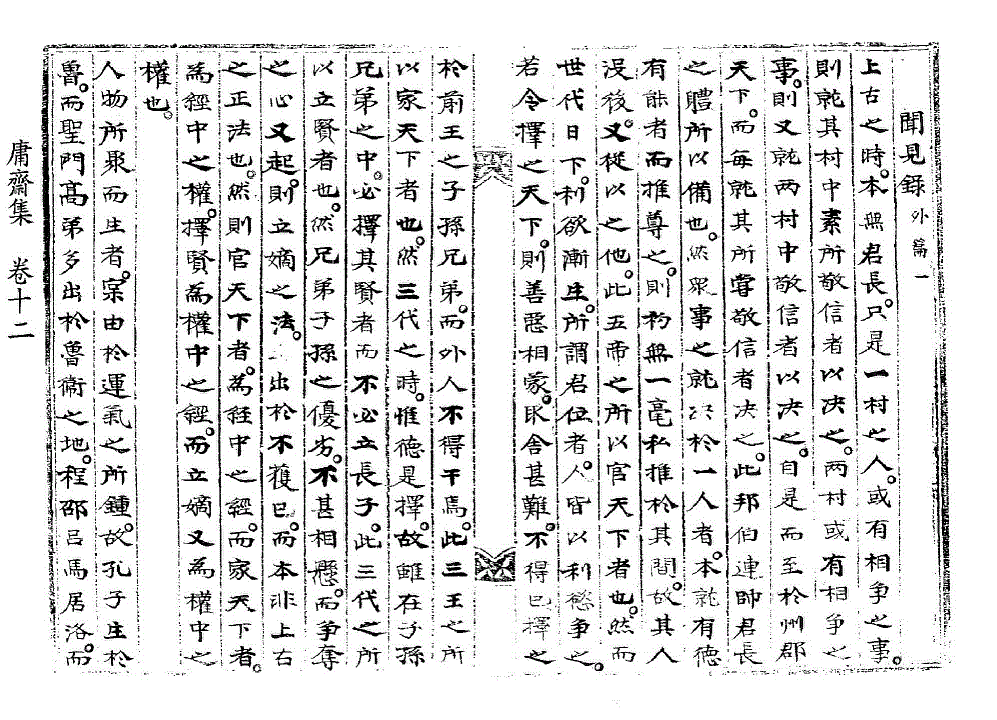 闻见录(外篇一)
闻见录(外篇一)上古之时。本无君长。只是一村之人。或有相争之事。则就其村中素所敬信者以决之。两村或有相争之事。则又就两村中敬信者以决之。自是而至于州郡天下。而每就其所尝敬信者决之。此邦伯连帅君长之体所以备也。然众事之就决于一人者。本就有德有能者而推尊之。则初无一毫私推于其间。故其人没后。又从以之他。此五帝之所以官天下者也。然而世代日下。利欲渐生。所谓君位者。人皆以利欲争之。若令择之天下。则善恶相蒙。取舍甚难。不得已择之于前王之子孙兄弟。而外人不得干焉。此三王之所以家天下者也。然三代之时。惟德是择。故虽在子孙兄弟之中。必择其贤者而不必立长子。此三代之所以立贤者也。然兄弟子孙之优劣。不甚相悬。而争夺之心又起。则立嫡之法。▦出于不获已。而本非上古之正法也。然则官天下者。为经中之经。而家天下者。为经中之权。择贤为权中之经。而立嫡又为权中之权也。
人物所聚而生者。宲由于运气之所钟。故孔子生于鲁。而圣门高弟多出于鲁卫之地。程邵吕马居洛。而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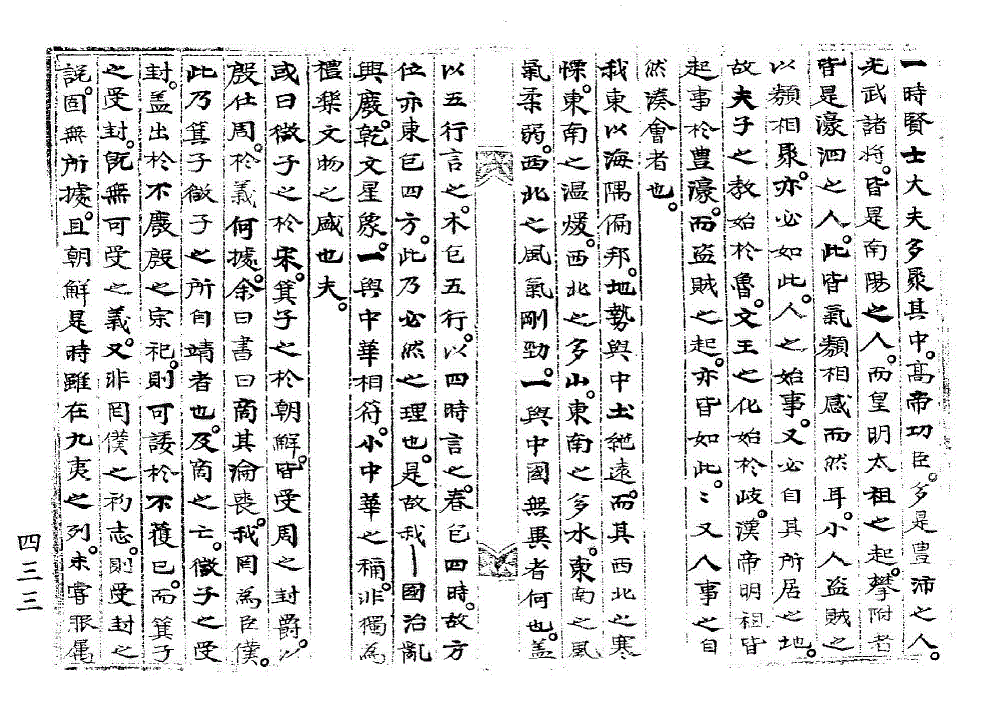 一时贤士大夫多聚其中。高帝功臣。多是礼沛之人。光武诸将。皆是南阳之人。而皇明太祖之起。攀附者皆是濠泗之人。此皆气类相感而然耳。小人盗贼之以类相聚。亦必如此。人之始事。又必自其所居之地。故夫子之教始于鲁。文王之化始于岐。汉帝明祖皆起事于礼濠。而盗贼之起。亦皆如此。此又人事之自然凑会者也。
一时贤士大夫多聚其中。高帝功臣。多是礼沛之人。光武诸将。皆是南阳之人。而皇明太祖之起。攀附者皆是濠泗之人。此皆气类相感而然耳。小人盗贼之以类相聚。亦必如此。人之始事。又必自其所居之地。故夫子之教始于鲁。文王之化始于岐。汉帝明祖皆起事于礼濠。而盗贼之起。亦皆如此。此又人事之自然凑会者也。我东以海隅偏邦。地势与中土绝远。而其西北之寒慄。东南之温煖。西北之多山。东南之多水。东南之风气柔弱。西北之风气刚劲。一与中国无异者何也。盖以五行言之。木包五行。以四时言之。春包四时。故方位亦东包四方。此乃必然之理也。是故我国治乱兴废。乾文星象。一与中华相符。小中华之称。非独为礼乐文物之盛也夫。
或曰微子之于宋。箕子之于朝鲜。皆受周之封爵。以殷仕周。于义何据。余曰书曰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此乃箕子微子之所自靖者也。及商之亡。微子之受封。盖出于不废殷之宗祀。则可诿于不获已。而箕子之受封。既无可受之义。又非罔仆之初志。则受封之说。固无所据。且朝鲜是时虽在九夷之列。未尝服属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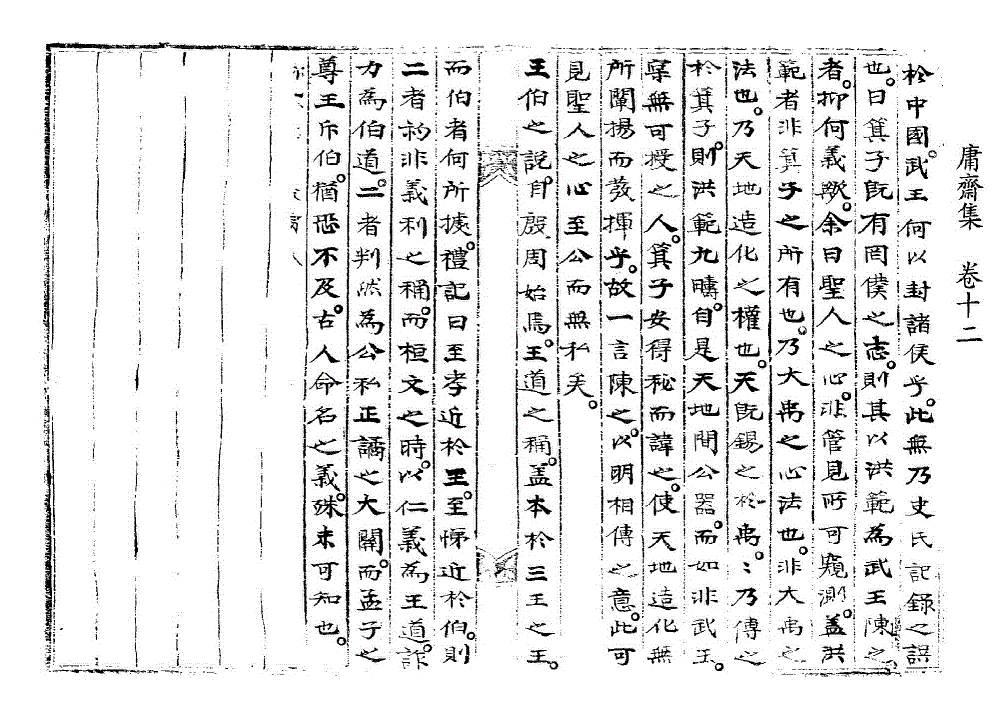 于中国。武王何以封诸侯乎。此无乃史氏记录之误也。曰箕子既有罔仆之志。则其以洪范为武王陈之者。抑何义欤。余曰圣人之心。非管见所可窥测。盖洪范者非箕子之所有也。乃大禹之心法也。非大禹之法也。乃天地造化之权也。天既锡之于禹。禹乃传之于箕子。则洪范九畴。自是天地间公器。而如非武王。宲无可授之人。箕子安得秘而讳之。使天地造化无所阐扬而发挥乎。故一言陈之。以明相传之意。此可见圣人之心至公而无私矣。
于中国。武王何以封诸侯乎。此无乃史氏记录之误也。曰箕子既有罔仆之志。则其以洪范为武王陈之者。抑何义欤。余曰圣人之心。非管见所可窥测。盖洪范者非箕子之所有也。乃大禹之心法也。非大禹之法也。乃天地造化之权也。天既锡之于禹。禹乃传之于箕子。则洪范九畴。自是天地间公器。而如非武王。宲无可授之人。箕子安得秘而讳之。使天地造化无所阐扬而发挥乎。故一言陈之。以明相传之意。此可见圣人之心至公而无私矣。王伯之说。自殷周始焉。王道之称。盖本于三王之王。而伯者何所据。礼记曰至孝近于王。至悌近于伯。则二者初非义利之称。而桓文之时。以仁义为王道。诈力为伯道。二者判然为公私正谲之大关。而孟子之尊王斥伯。犹恐不及。古人命名之义。殊未可知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4L 页
 南华经内七篇。一条说去。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详密。庄周之道。非为独善其身。盖欲达之天下。故七篇命意。与大学八条目。略略相似。大抵逍遥游者。极言道体之大。即大学格致之工也。齐物论者。一齐万物。归于虚无。即大学诚意之工也。养生主者。始养心神。不为物累。即大学正心之工也。人间世者。日用行事之谓。即大学修身之工也。德充符者。德之充于内而符于外者。即大学齐家之工也。大宗师者。道成而大为民师。即大学治国之工也。应帝王者。以道应乎帝王之治者。即大学平天下之工也。读者不可不知此也。
南华经内七篇。一条说去。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详密。庄周之道。非为独善其身。盖欲达之天下。故七篇命意。与大学八条目。略略相似。大抵逍遥游者。极言道体之大。即大学格致之工也。齐物论者。一齐万物。归于虚无。即大学诚意之工也。养生主者。始养心神。不为物累。即大学正心之工也。人间世者。日用行事之谓。即大学修身之工也。德充符者。德之充于内而符于外者。即大学齐家之工也。大宗师者。道成而大为民师。即大学治国之工也。应帝王者。以道应乎帝王之治者。即大学平天下之工也。读者不可不知此也。朱子地浮水面之说。东儒多疑之。或以为记录之误。余则以为非误录也。夫地者即天中一物。其形如斗。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其四方及下面。如非积水所涵。必是空虚茫荡。如其空虚。必有物。如云有物。则即利马窦六面世界之说。是岂理也哉。夫五行之生。水为之首。八卦之成。水居其一。而自天地混沦之初。即一湿气。物于天地。莫大于水。其所包涵大地。亦理之常。夫何足疑。然古人有曰地之在水面。升降往来随四时。各适四方者。此恐未然。夫天者阳也。阳以动为体。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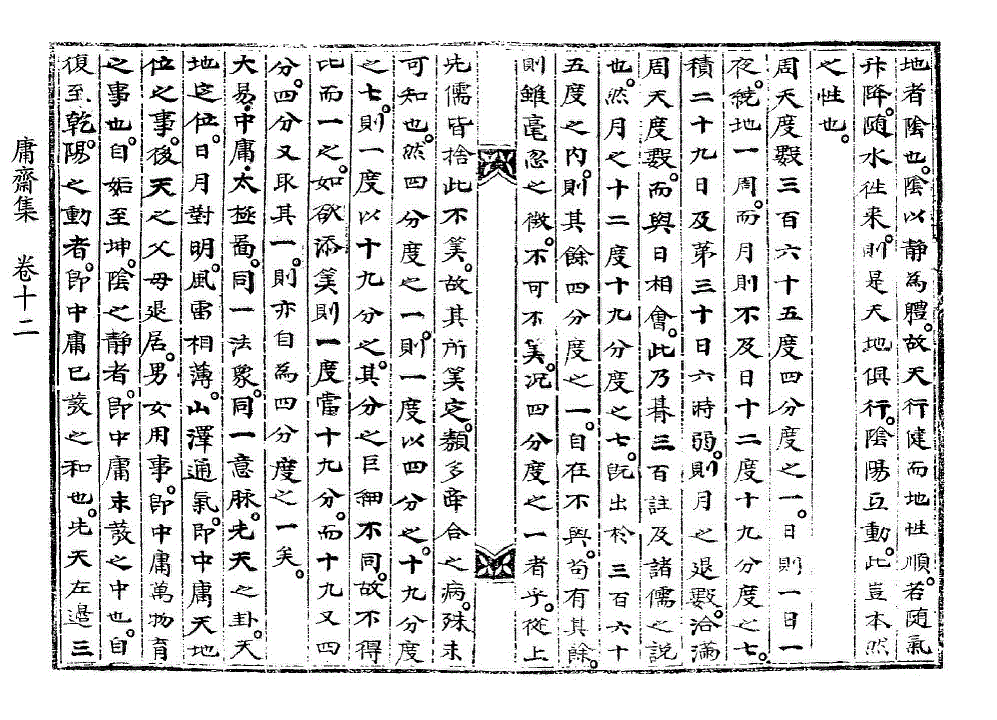 地者阴也。阴以静为体。故天行健而地性顺。若随气升降。随水往来。则是天地俱行。阴阳互动。此岂本然之性也。
地者阴也。阴以静为体。故天行健而地性顺。若随气升降。随水往来。则是天地俱行。阴阳互动。此岂本然之性也。周天度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则一日一夜。绕地一周。而月则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积二十九日及第三十日六时弱。则月之退数。洽满周天度数。而与日相会。此乃期三百注及诸儒之说也。然月之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既出于三百六十五度之内。则其馀四分度之一。自在不与。苟有其馀。则虽毫忽之微。不可不算。况四分度之一者乎。从上先儒皆舍此不算。故其所算定。类多牵合之病。殊未可知也。然四分度之一。则一度以四分之。十九分度之七。则一度以十九分之。其分之巨细不同。故不得比而一之。如欲添算则一度当十九分。而十九又四分。四分又取其一。则亦自为四分度之一矣。
大易,中庸,太极啚。同一法象。同一意脉。先天之卦。天地定位。日月对明。风雷相薄。山泽通气。即中庸天地位之事。后天之父母退居。男女用事。即中庸万物育之事也。自姤至坤。阴之静者。即中庸未发之中也。自复至乾。阳之动者。即中庸已发之和也。先天左边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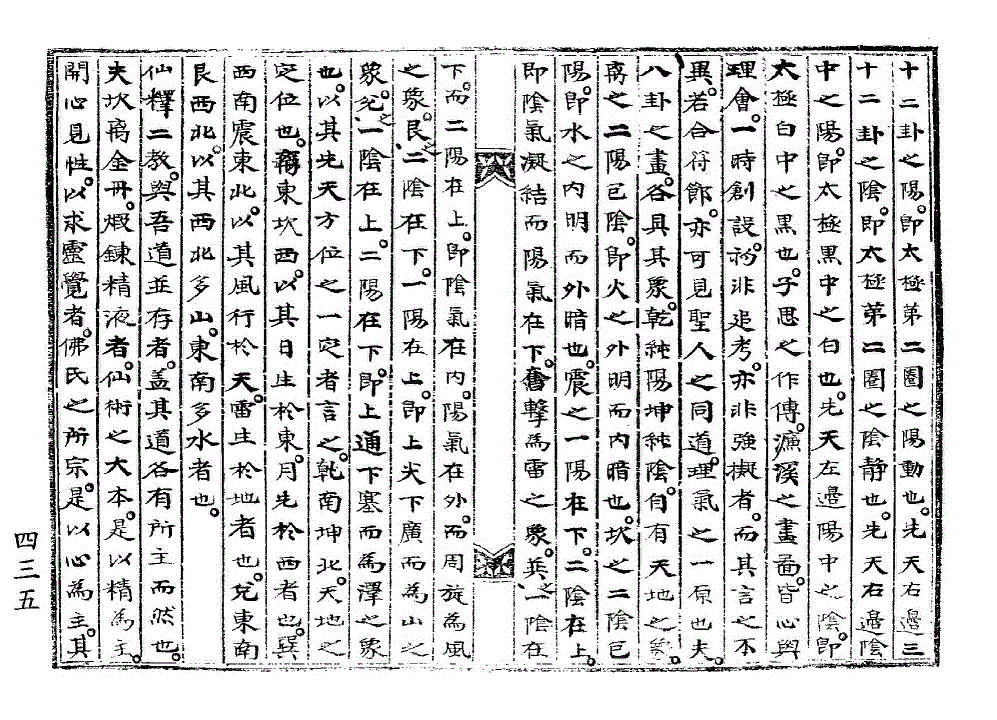 十二卦之阳。即太极第二圈之阳动也。先天右边三十二卦之阴。即太极第二圈之阴静也。先天右边阴中之阳。即太极黑中之白也。先天左边阳中之阴。即太极白中之黑也。子思之作传。濂溪之画啚。皆心与理会。一时创设。初非追考。亦非强拟者。而其言之不异。若合符节。亦可见圣人之同道。理气之一原也夫。八卦之画。各具其象。乾纯阳坤纯阴。自有天地之象。离之二阳包阴。即火之外明而内暗也。坎之二阴包阳。即水之内明而外暗也。震之一阳在下。二阴在上。即阴气凝结而阳气在下。奋击为雷之象。巽之一阴在下。而二阳在上。即阴气在内。阳气在外。而周旋为风之象。艮之二阴在下。一阳在上。即上尖下广而为山之象。兑之一阴在上。二阳在下。即上通下塞而为泽之象也。以其先天方位之一定者言之。乾南坤北。天地之定位也。离东坎西。以其日生于东。月先于西者也。巽西南震东北。以其风行于天。雷生于地者也。兑东南艮西北。以其西北多山。东南多水者也。
十二卦之阳。即太极第二圈之阳动也。先天右边三十二卦之阴。即太极第二圈之阴静也。先天右边阴中之阳。即太极黑中之白也。先天左边阳中之阴。即太极白中之黑也。子思之作传。濂溪之画啚。皆心与理会。一时创设。初非追考。亦非强拟者。而其言之不异。若合符节。亦可见圣人之同道。理气之一原也夫。八卦之画。各具其象。乾纯阳坤纯阴。自有天地之象。离之二阳包阴。即火之外明而内暗也。坎之二阴包阳。即水之内明而外暗也。震之一阳在下。二阴在上。即阴气凝结而阳气在下。奋击为雷之象。巽之一阴在下。而二阳在上。即阴气在内。阳气在外。而周旋为风之象。艮之二阴在下。一阳在上。即上尖下广而为山之象。兑之一阴在上。二阳在下。即上通下塞而为泽之象也。以其先天方位之一定者言之。乾南坤北。天地之定位也。离东坎西。以其日生于东。月先于西者也。巽西南震东北。以其风行于天。雷生于地者也。兑东南艮西北。以其西北多山。东南多水者也。仙释二教。与吾道并存者。盖其道各有所主而然也。夫坎离金丹。煅鍊精液者。仙术之大本。是以精为主。开心见性。以求灵觉者。佛氏之所宗。是以心为主。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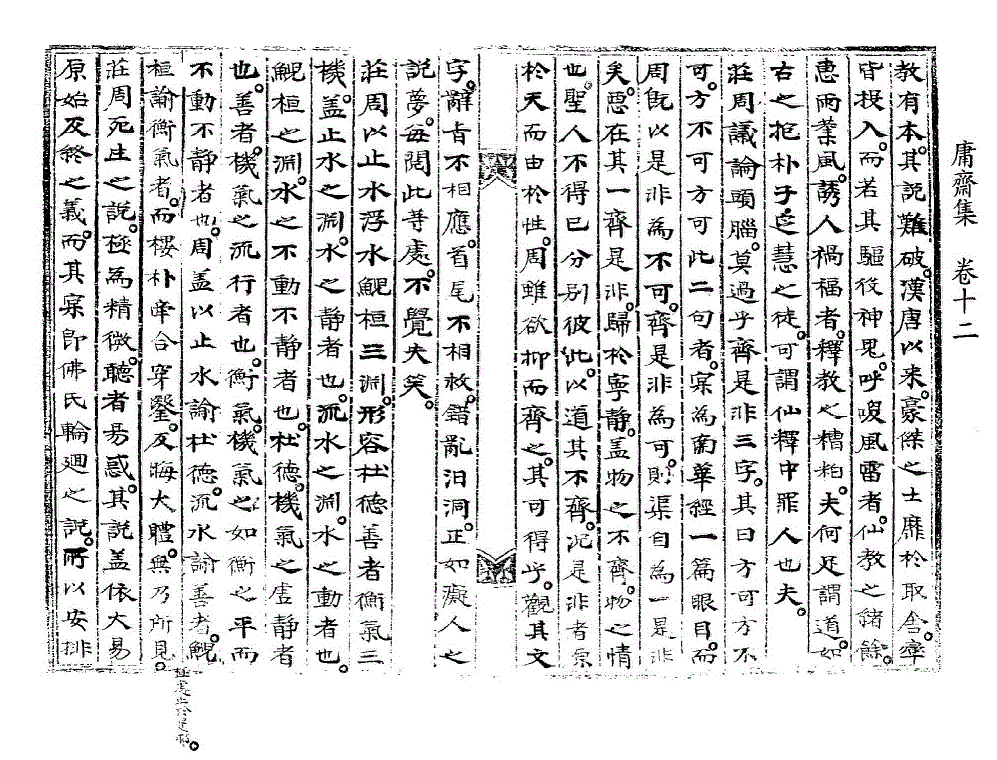 教有本。其说难破。汉唐以来。豪杰之士靡于取舍。率皆投入。而若其驱役神鬼。呼唤风雷者。仙教之绪馀。惠雨业风。诱人祸福者。释教之糟粕。夫何足谓道。如古之抱朴子,定慧之徒。可谓仙释中罪人也夫。
教有本。其说难破。汉唐以来。豪杰之士靡于取舍。率皆投入。而若其驱役神鬼。呼唤风雷者。仙教之绪馀。惠雨业风。诱人祸福者。释教之糟粕。夫何足谓道。如古之抱朴子,定慧之徒。可谓仙释中罪人也夫。庄周议论头脑。莫过乎齐是非三字。其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此二句者。宲为南华经一篇眼目。而周既以是非为不可。齐是非为可。则渠自为一是非矣。恶在其一齐是非。归于宁静。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圣人不得已分别彼此。以道其不齐。况是非者原于天而由于性。周虽欲抑而齐之。其可得乎。观其文字。辞旨不相应。首尾不相救。错乱汩洞。正如痴人之说梦。每阅此等处。不觉失笑。
庄周以止水浮水鲵桓三渊。形容杜德善者衡气三机。盖止水之渊。水之静者也。流水之渊。水之动者也。鲵桓之渊。水之不动不静者也。杜德。机气之虚静者也。善者。机气之流行者也。衡气。机气之如衡之平而不动不静者也。周盖以止水谕杜德。流水谕善者。鲵桓谕衡气者。而楼朴牵合穿凿。反晦大体。无乃所见。极处止于是耶。庄周死生之说。极为精微。听者易惑。其说盖依大易原始反终之义。而其宲即佛氏轮回之说。所以安排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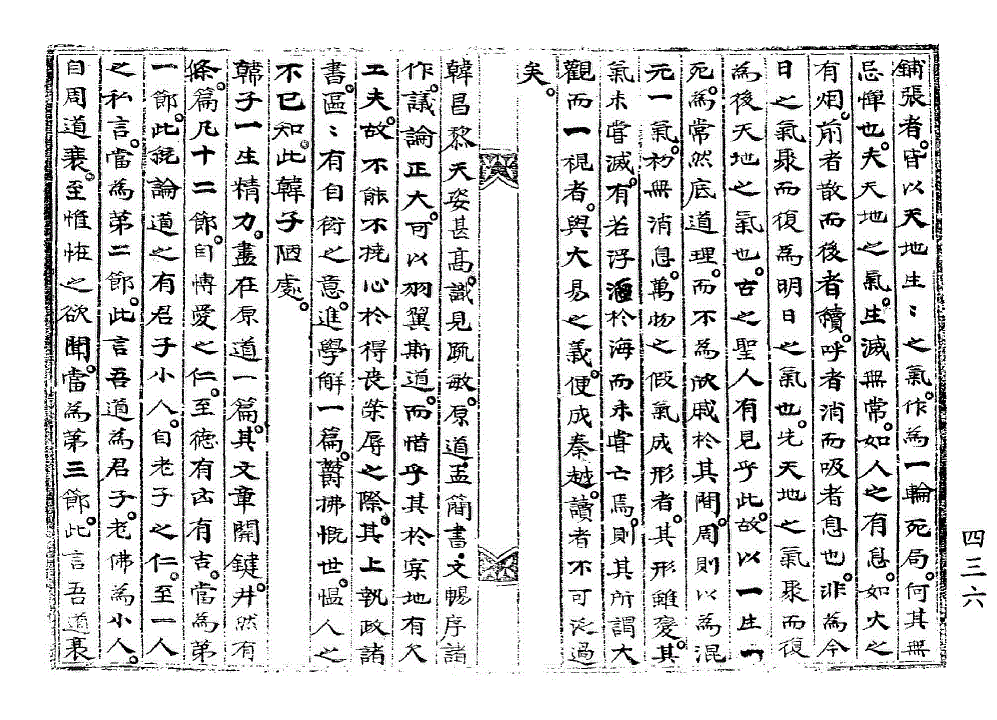 铺张者。皆以天地生生之气。作为一轮死局。何其无忌惮也。夫天地之气。生灭无常。如人之有息。如火之有烟。前者散而后者续。呼者消而吸者息也。非为今日之气聚而复为明日之气也。先天地之气聚而复为后天地之气也。古之圣人有见乎此。故以一生一死。为常然底道理。而不为欣戚于其间。周则以为混元一气。初无消息。万物之假气成形者。其形虽变。其气未尝灭。有若浮沤于海而未尝亡焉。则其所谓大观而一视者。与大易之义。便成秦越。读者不可泛过矣。
铺张者。皆以天地生生之气。作为一轮死局。何其无忌惮也。夫天地之气。生灭无常。如人之有息。如火之有烟。前者散而后者续。呼者消而吸者息也。非为今日之气聚而复为明日之气也。先天地之气聚而复为后天地之气也。古之圣人有见乎此。故以一生一死。为常然底道理。而不为欣戚于其间。周则以为混元一气。初无消息。万物之假气成形者。其形虽变。其气未尝灭。有若浮沤于海而未尝亡焉。则其所谓大观而一视者。与大易之义。便成秦越。读者不可泛过矣。韩昌黎天姿甚高。识见疏敏。原道,孟简书,文畅序诸作。议论正大。可以羽翼斯道。而惜乎其于宲地有欠工夫。故不能不挠心于得丧荣辱之际。其上执政诸书。区区有自衒之意。进学解一篇。郁拂慨世。愠人之不己知。此韩子陋处。
韩子一生精力。尽在原道一篇。其文章关键。井然有条。篇凡十二节。自博爱之仁。至德有凶有吉。当为第一节。此统论道之有君子小人。自老子之仁。至一人之私言。当为第二节。此言吾道为君子。老佛为小人。自周道衰。至惟怪之欲闻。当为第三节。此言吾道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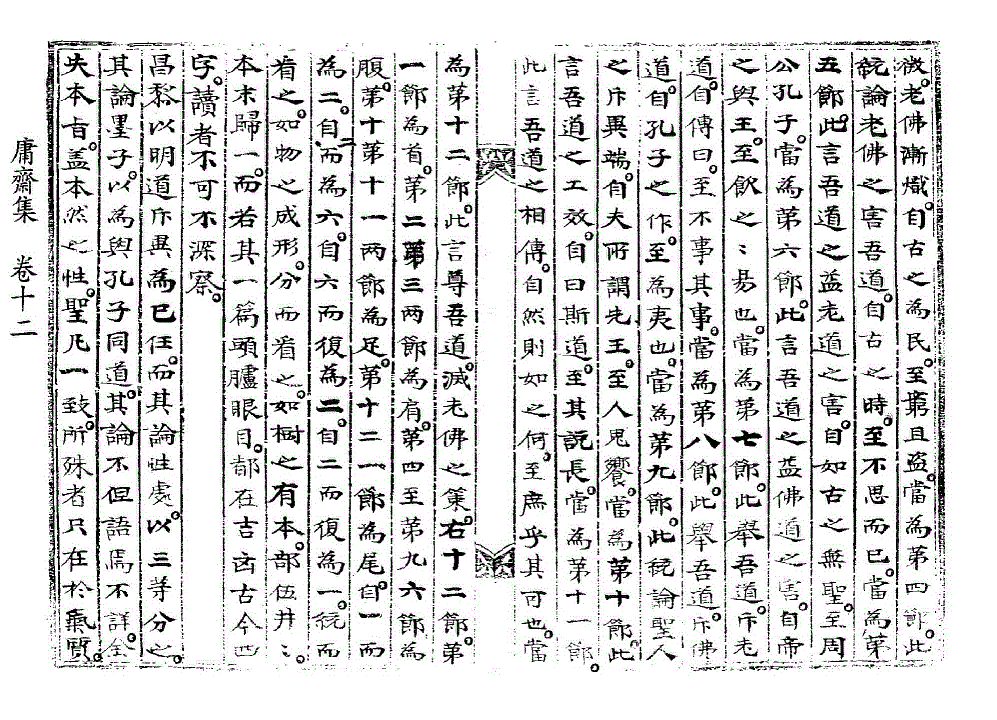 微。老佛渐炽。自古之为民。至穷且盗。当为第四节。此统论老佛之害吾道。自古之时。至不思而已。当为第五节。此言吾道之益老道之害。自如古之无圣。至周公孔子。当为第六节。此言吾道之益佛道之害。自帝之与王。至饮之之易也。当为第七节。此举吾道。斥老道。自传曰。至不事其事。当为第八节。此举吾道。斥佛道。自孔子之作。至为夷也。当为第九节。此统论圣人之斥异端。自夫所谓先王。至人鬼飨。当为第十节。此言吾道之工效。自曰斯道。至其说长。当为第十一节。此言吾道之相传。自然则如之何。至庶乎其可也。当为第十二节。此言尊吾道。灭老佛之策。右十二节。第一节为首。第二第三两节为肩。第四至第九六节为腹。第十第十一两节为足。第十二一节为尾。自一而为二。自二而为六。自六而复为二。自二而复为一。统而看之。如物之成形。分而看之。如树之有本。部伍井井。本末归一。而若其一篇头胪眼目。都在吉凶古今四字。读者不可不深察。
微。老佛渐炽。自古之为民。至穷且盗。当为第四节。此统论老佛之害吾道。自古之时。至不思而已。当为第五节。此言吾道之益老道之害。自如古之无圣。至周公孔子。当为第六节。此言吾道之益佛道之害。自帝之与王。至饮之之易也。当为第七节。此举吾道。斥老道。自传曰。至不事其事。当为第八节。此举吾道。斥佛道。自孔子之作。至为夷也。当为第九节。此统论圣人之斥异端。自夫所谓先王。至人鬼飨。当为第十节。此言吾道之工效。自曰斯道。至其说长。当为第十一节。此言吾道之相传。自然则如之何。至庶乎其可也。当为第十二节。此言尊吾道。灭老佛之策。右十二节。第一节为首。第二第三两节为肩。第四至第九六节为腹。第十第十一两节为足。第十二一节为尾。自一而为二。自二而为六。自六而复为二。自二而复为一。统而看之。如物之成形。分而看之。如树之有本。部伍井井。本末归一。而若其一篇头胪眼目。都在吉凶古今四字。读者不可不深察。昌黎以明道斥异为己任。而其论性处。以三等分之。其论墨子。以为与孔子同道。其论不但语焉不详。全失本旨。盖本然之性。圣凡一致。所殊者只在于气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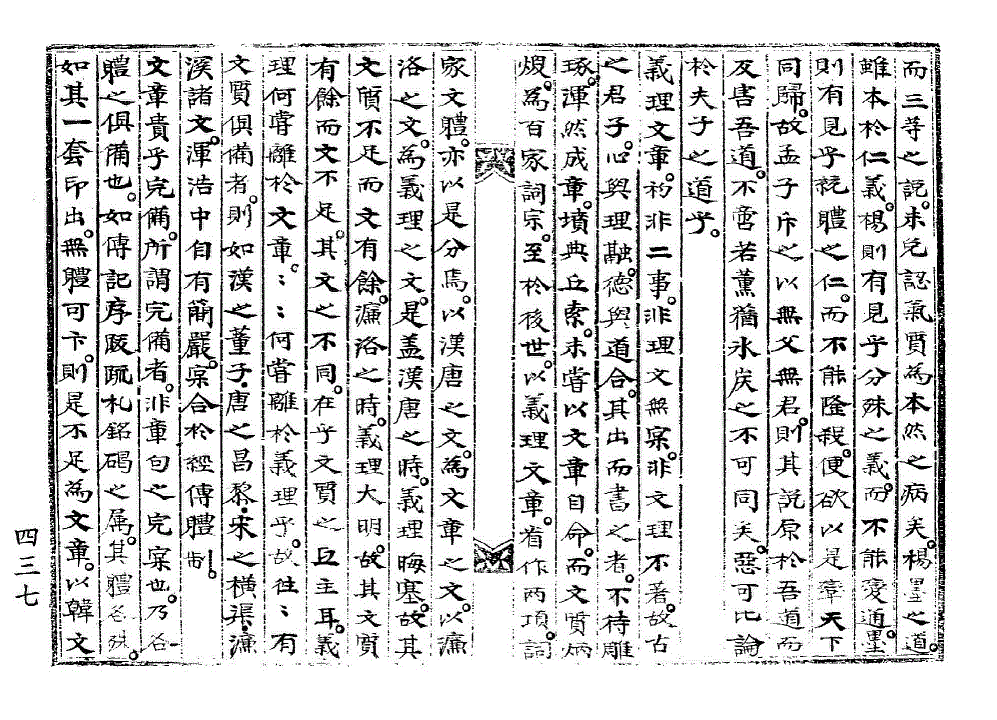 而三等之说。未免认气质为本然之病矣。杨墨之道。虽本于仁义。杨则有见乎分殊之义。而不能变通。墨则有见乎统体之仁。而不能隆杀。便欲以是率天下同归。故孟子斥之以无父无君。则其说原于吾道而反害吾道。不啻若薰莸冰炭之不可同矣。恶可比论于夫子之道乎。
而三等之说。未免认气质为本然之病矣。杨墨之道。虽本于仁义。杨则有见乎分殊之义。而不能变通。墨则有见乎统体之仁。而不能隆杀。便欲以是率天下同归。故孟子斥之以无父无君。则其说原于吾道而反害吾道。不啻若薰莸冰炭之不可同矣。恶可比论于夫子之道乎。义理文章。初非二事。非理文无宲。非文理不著。故古之君子。心与理融。德与道合。其出而书之者。不待雕琢。浑然成章。坟典丘索。未尝以文章自命。而文质炳焕。为百家词宗。至于后世。以义理文章。看作两项。词家文体。亦以是分焉。以汉唐之文。为文章之文。以濂洛之文。为义理之文。是盖汉唐之时。义理晦塞。故其文质不足而文有馀。濂洛之时。义理大明。故其文质有馀而文不足。其文之不同。在乎文质之互主耳。义理何尝离于文章。文章何尝离于义理乎。故往往有文质俱备者。则如汉之蕫子,唐之昌黎,宋之横渠,濂溪诸文。浑浩中自有简严。宲合于经传体制。
文章贵乎完备。所谓完备者。非章句之完宲也。乃各体之俱备也。如传记序跋疏札铭碣之属。其体各殊。如其一套印出。无体可卞。则是不足为文章。以韩文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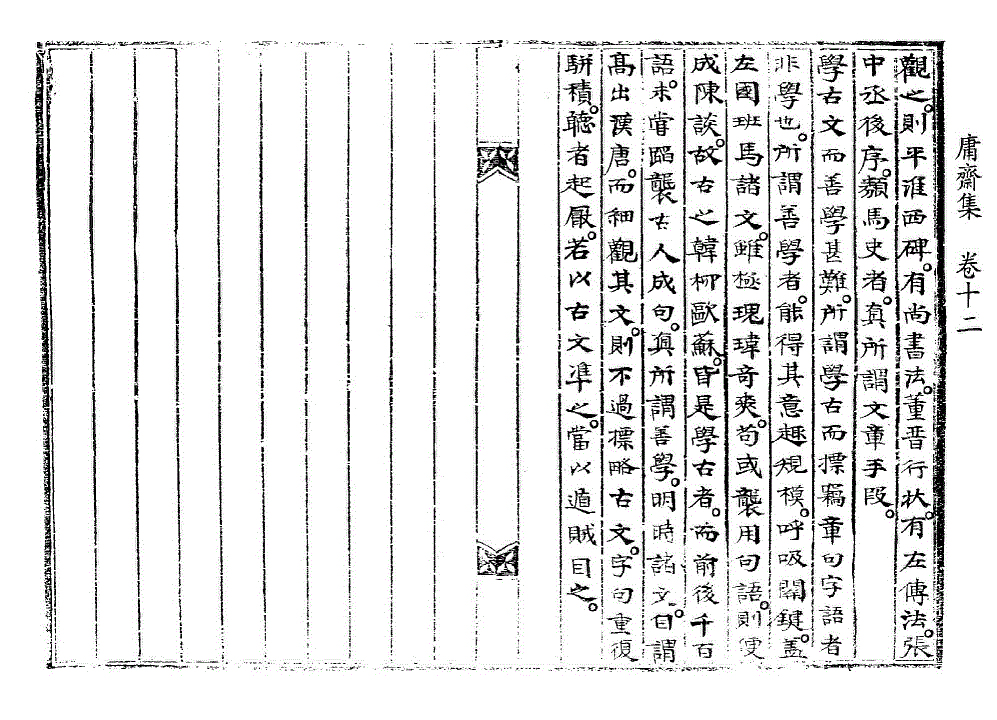 观之。则平淮西碑。有尚书法。董晋行状。有左传法。张中丞后序。类马史者。真所谓文章手段。
观之。则平淮西碑。有尚书法。董晋行状。有左传法。张中丞后序。类马史者。真所谓文章手段。学古文而善学甚难。所谓学古而摽窃章句字语者非学也。所谓善学者。能得其意趣规模。呼吸关键。盖左国班马诸文。虽极瑰玮奇爽。苟或袭用句语。则便成陈谈。故古之韩柳欧苏。皆是学古者。而前后千百语。未尝蹈袭古人成句。真所谓善学。明时诸文。自谓高出汉唐。而细观其文。则不过摽略古文。字句重复骈积。听者起厌。若以古文准之。当以遁贼目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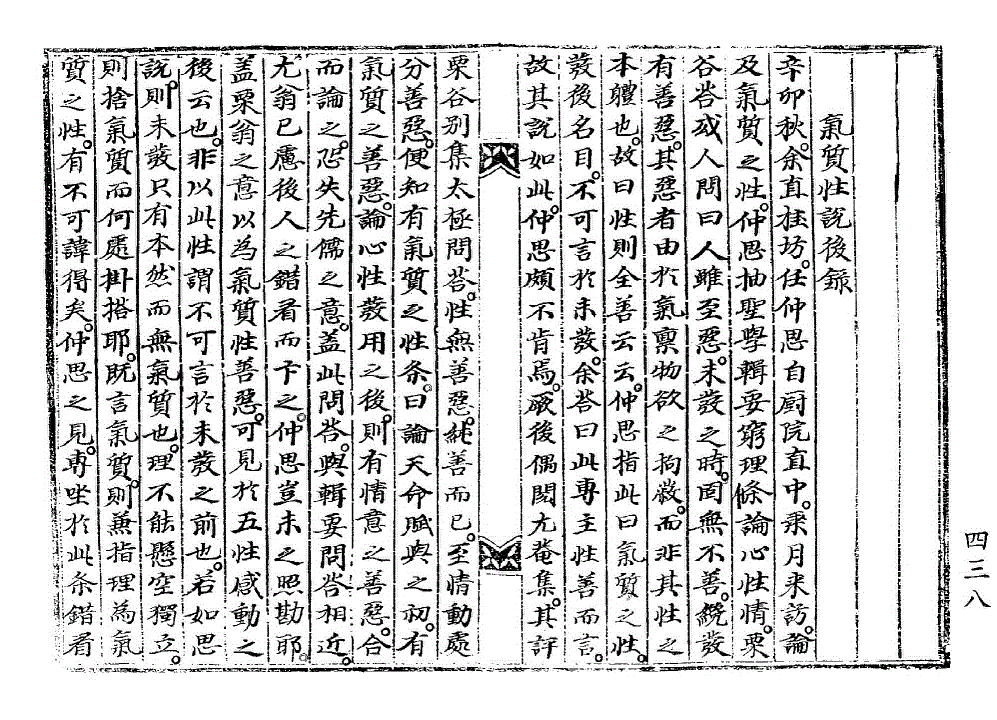 气质性说后录
气质性说后录辛卯秋。余直桂坊。任仲思自厨院直中。乘月来访。论及气质之性。仲思抽圣学辑要穷理条论心性情。栗谷答或人问曰人虽至恶。未发之时。固无不善。才发有善恶。其恶者由于气禀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体也。故曰性则全善云云。仲思指此曰气质之性。发后名目。不可言于未发。余答曰此专主性善而言。故其说如此。仲思颇不肯焉。厥后偶阅尤庵集。其评栗谷别集太极问答。性无善恶。纯善而已。至情动处分善恶。便知有气质之性条。曰论天命赋与之初。有气质之善恶。论心性发用之后。则有情意之善恶。合而论之。恐失先儒之意。盖此问答。与辑要问答相近。尤翁已虑后人之错看而卞之。仲思岂未之照勘耶。盖栗翁之意以为气质性善恶。可见于五性感动之后云也。非以此性谓不可言于未发之前也。若如思说。则未发只有本然而无气质也。理不能悬空独立。则舍气质而何处挂搭耶。既言气质。则兼指理为气质之性。有不可讳得矣。仲思之见。专坐于此条错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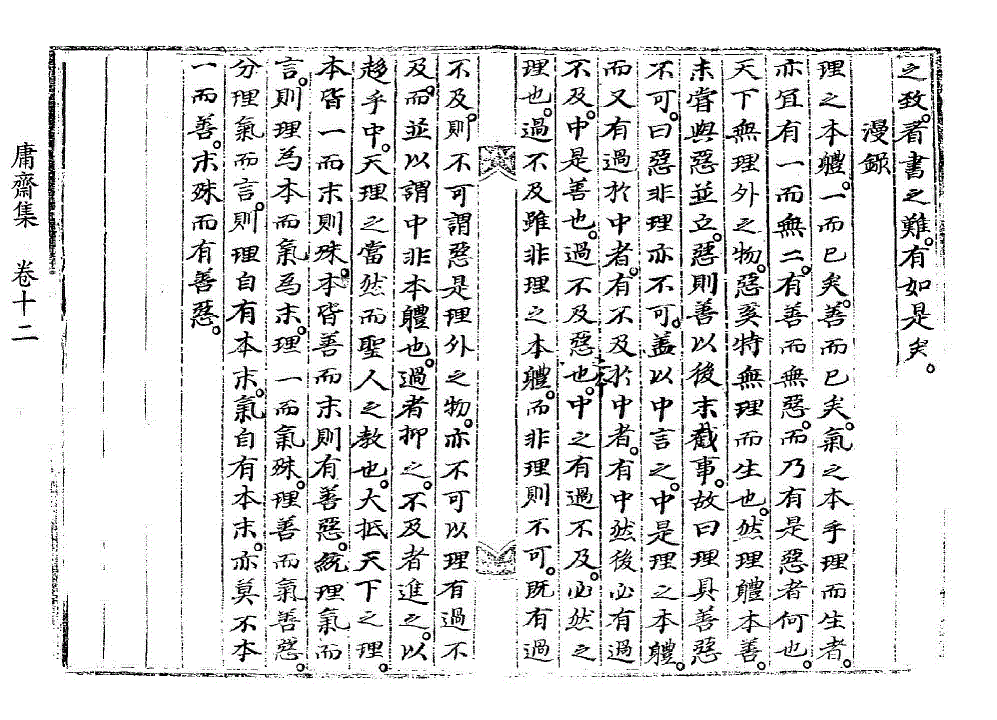 之致。看书之难。有如是矣。
之致。看书之难。有如是矣。漫录
理之本体。一而已矣。善而已矣。气之本乎理而生者。亦宜有一而无二。有善而无恶。而乃有是恶者何也。天下无理外之物。恶奚特无理而生也。然理体本善。未尝与恶并立。恶则善以后末截事。故曰理具善恶不可。曰恶非理亦不可。盖以中言之。中是理之本体。而又有过于中者。有不及于中者。有中然后必有过不及。中是善也。过不及恶之本也。中之有过不及。必然之理也。过不及虽非理之本体。而非理则不可。既有过不及。则不可谓恶是理外之物。亦不可以理有过不及。而并以谓中非本体也。过者抑之。不及者进之。以趍乎中。天理之当然而圣人之教也。大抵天下之理。本皆一而末则殊。本皆善而末则有善恶。统理气而言。则理为本而气为末。理一而气殊。理善而气善恶。分理气而言。则理自有本末。气自有本末。亦莫不本一而善。末殊而有善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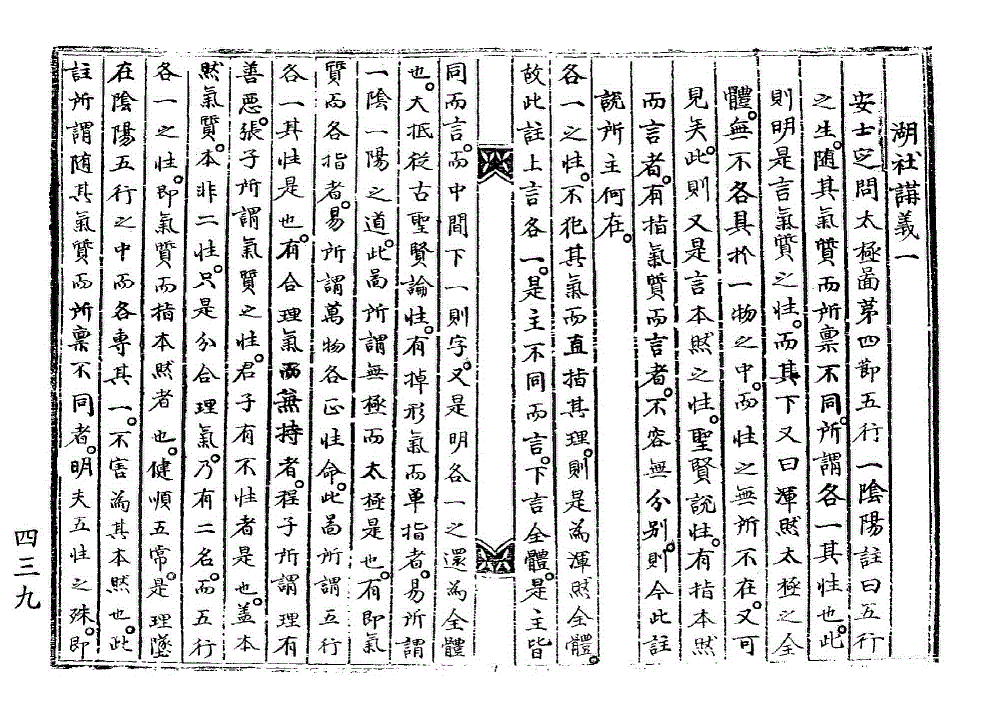 湖社讲义[一]
湖社讲义[一]安士定问太极啚第四节五行一阴阳注曰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此则明是言气质之性。而其下又曰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此则又是言本然之性。圣贤说性。有指本然而言者。有指气质而言者。不容无分别。则今此注说所主何在。
各一之性。不犯其气而直指其理。则是为浑然全体。故此注上言各一。是主不同而言。下言全体。是主皆同而言。而中间下一则字。又是明各一之还为全体也。大抵从古圣贤论性。有掉形气而单指者。易所谓一阴一阳之道。此啚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也。有即气质而各指者。易所谓万物各正性命。此啚所谓五行各一其性是也。有合理气而兼持者。程子所谓理有善恶。张子所谓气质之性。君子有不性者是也。盖本然气质。本非二性。只是分合理气。乃有二名。而五行各一之性。即气质而指本然者也。健顺五常。是理坠在阴阳五行之中而各专其一。不害为其本然也。此注所谓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者。明夫五性之殊。即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H 页
 因气质之异也。所谓太极全体无不各具者。明夫五常之德。莫非本然之理也。故愚以为五行各一之性。对太极一原之理而言。则当为气质之性。对气质善恶之性而言。则当为本然之性。知此说者。可与论性矣。
因气质之异也。所谓太极全体无不各具者。明夫五常之德。莫非本然之理也。故愚以为五行各一之性。对太极一原之理而言。则当为气质之性。对气质善恶之性而言。则当为本然之性。知此说者。可与论性矣。第七节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天地日月。固可谓相合。而四时鬼神之合。未知指何事而言耶。伏愿诸君子明赐开释也。
大则教化生成。小则动静语嘿。圣人之序。合乎四时者也。大则劝赏惩讨。小则喜怒舒惨。圣人之吉凶。合乎鬼神者也。天人虽殊。其理则一也。
洪祖东问论语子路问鬼神章。程子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朱子小注曰一是理。二是气。一二之义。可得闻其详欤。
死生二气。而死生之道一也。人鬼二气而人鬼之道一也。一而二者。先言理而后言气也。二而一者。先言气而后言理也。程朱之意。恐或如是耶。
道心原于性命之正。人心生于形气之私。谓人心之善者为道心。则人心道心无别。而人心偏于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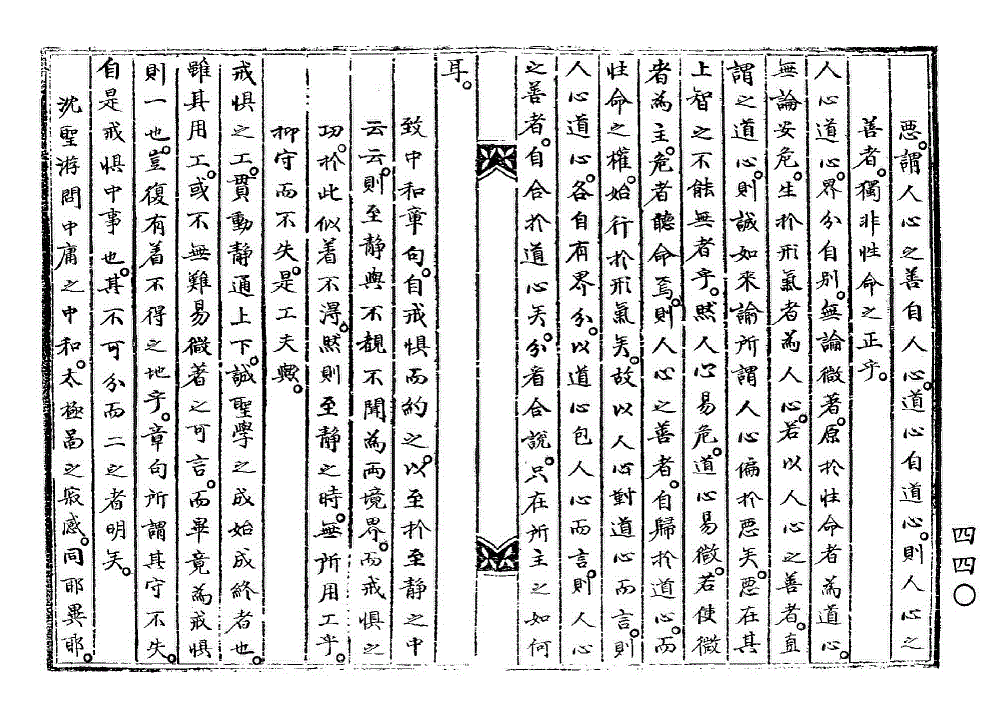 恶。谓人心之善自人心。道心自道心。则人心之善者。独非性命之正乎。
恶。谓人心之善自人心。道心自道心。则人心之善者。独非性命之正乎。人心道心。界分自别。无论微著。原于性命者为道心。无论安危。生于形气者为人心。若以人心之善者。直谓之道心。则诚如来谕所谓人心偏于恶矣。恶在其上智之不能无者乎。然人心易危。道心易微。若使微者为主。危者听命焉。则人心之善者。自归于道心。而性命之权。始行于形气矣。故以人心对道心而言。则人心道心。各自有界分。以道心包人心而言。则人心之善者。自合于道心矣。分看合说。只在所主之如何耳。
致中和章句。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云云。则至静与不睹不闻为两境界。而戒惧之功。于此似着不得。然则至静之时。无所用工乎。抑守而不失。是工夫欤。
戒惧之工。贯动静通上下。诚圣学之成始成终者也。虽其用工。或不无难易微著之可言。而毕竟为戒惧则一也。岂复有着不得之地乎。章句所谓其守不失。自是戒惧中事也。其不可分而二之者明矣。
沈圣游问中庸之中和。太极啚之寂感。同耶异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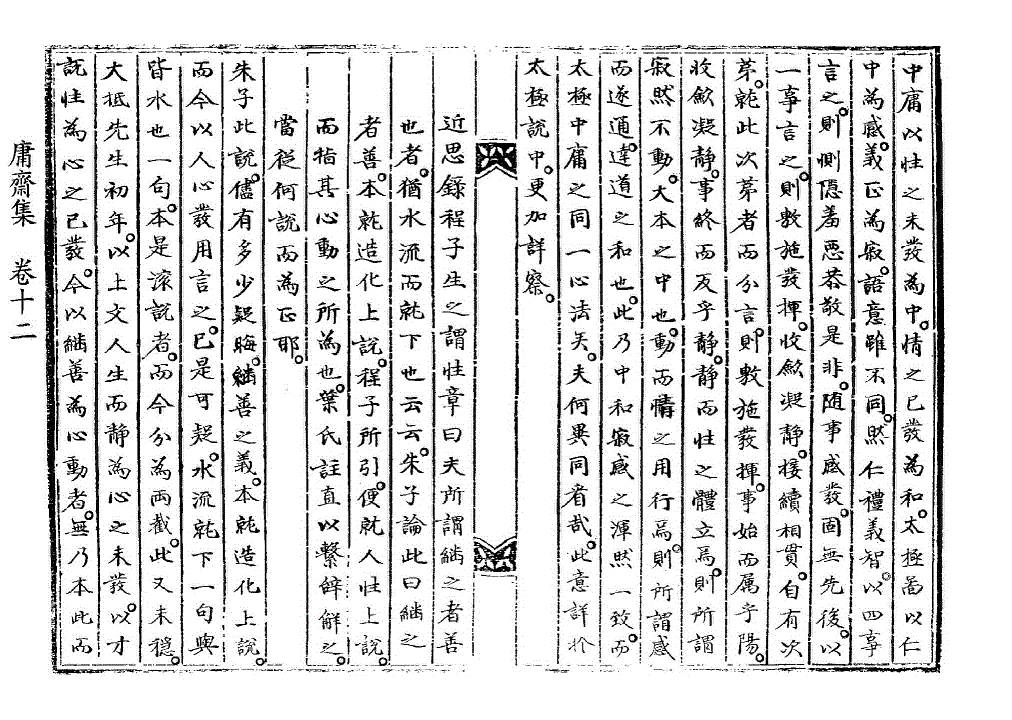 中庸以性之未发为中。情之已发为和。太极啚以仁中为感。义正为寂。语意虽不同。然仁礼义智。以四事言之。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随事感发。固无先后。以一事言之。则敷施发挥。收敛凝静。接续相贯。自有次第。就此次第者而分言。则敷施发挥。事始而属乎阳。收敛凝静。事终而反乎静。静而性之体立焉。则所谓寂然不动。大本之中也。动而情之用行焉。则所谓感而遂通。达道之和也。此乃中和寂感之浑然一致。而太极中庸之同一心法矣。夫何异同看哉。此意详于太极说中。更加详察。
中庸以性之未发为中。情之已发为和。太极啚以仁中为感。义正为寂。语意虽不同。然仁礼义智。以四事言之。则恻隐羞恶恭敬是非。随事感发。固无先后。以一事言之。则敷施发挥。收敛凝静。接续相贯。自有次第。就此次第者而分言。则敷施发挥。事始而属乎阳。收敛凝静。事终而反乎静。静而性之体立焉。则所谓寂然不动。大本之中也。动而情之用行焉。则所谓感而遂通。达道之和也。此乃中和寂感之浑然一致。而太极中庸之同一心法矣。夫何异同看哉。此意详于太极说中。更加详察。近思录程子生之谓性章曰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云云。朱子论此曰继之者善。本就造化上说。程子所引。便就人性上说。而指其心动之所为也。叶氏注直以系辞解之。当从何说而为正耶。
朱子此说。尽有多少疑晦。继善之义。本就造化上说。而今以人心发用言之。已是可疑。水流就下一句与皆水也一句。本是滚说者。而今分为两截。此又未稳。大抵先生初年。以上文人生而静为心之未发。以才说性为心之已发。今以继善为心动者。无乃本此而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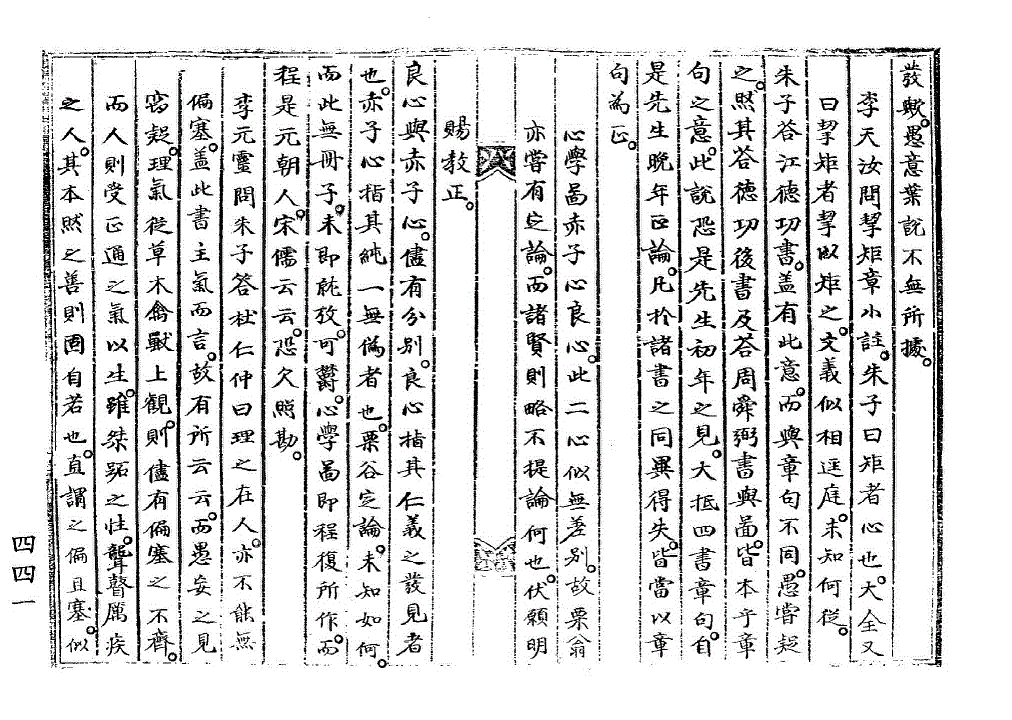 发欤。愚意叶说不无所据。
发欤。愚意叶说不无所据。李天汝问挈矩章小注。朱子曰矩者心也。大全又曰挈矩者挈以矩之。文义似相径庭。未知何从。
朱子答江德功书。盖有此意。而与章句不同。愚尝疑之。然其答德功后书及答周舜弼书与啚。皆本乎章句之意。此说恐是先生初年之见。大抵四书章句。自是先生晚年正论。凡于诸书之同异得失。皆当以章句为正。
心学啚赤子心良心。此二心似无差别。故栗翁亦尝有定论。而诸贤则略不提论何也。伏愿明赐教正。
良心与赤子心。尽有分别。良心指其仁义之发见者也。赤子心指其纯一无伪者也。栗谷定论。未知如何。而此无册子。未即就考。可郁。心学啚即程复所作。而程是元朝人。宋儒云云。恐欠照勘。
李元灵问朱子答杜仁仲曰理之在人。亦不能无偏塞。盖此书主气而言。故有所云云。而愚妄之见窃疑。理气从草木禽兽上观。则尽有偏塞之不齐。而人则受正通之气以生。虽桀蹠之性。聋瞽厉疾之人。其本然之善则固自若也。直谓之偏且塞。似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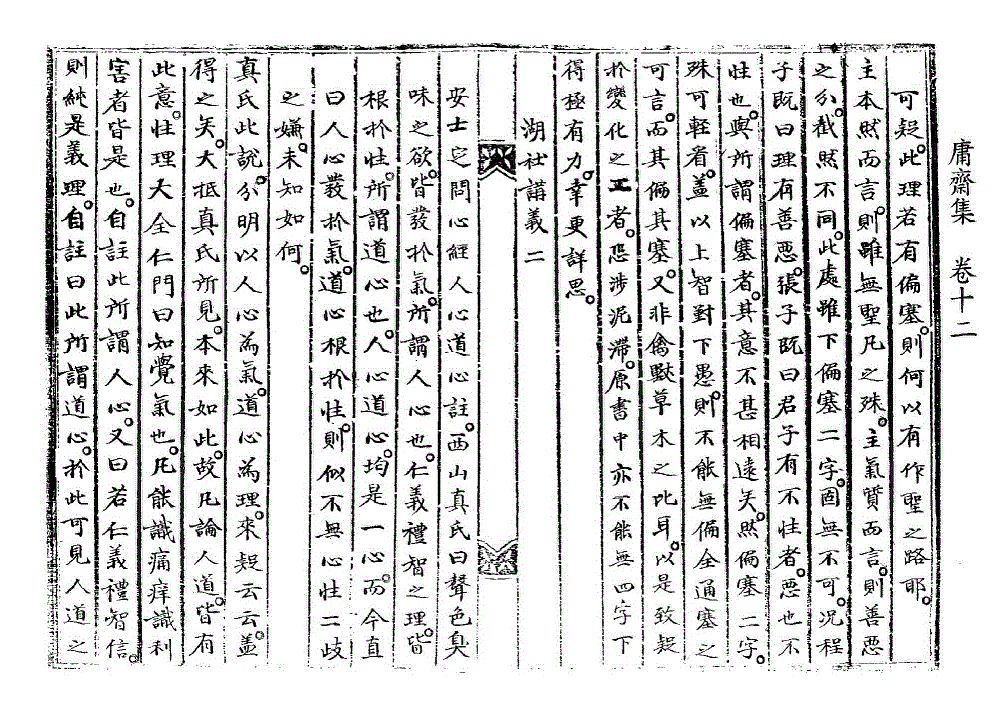 可疑。此理若有偏塞。则何以有作圣之路耶。
可疑。此理若有偏塞。则何以有作圣之路耶。主本然而言。则虽无圣凡之殊。主气质而言。则善恶之分。截然不同。此处虽下偏塞二字。固无不可。况程子既曰理有善恶。张子既曰君子有不性者。恶也不性也。与所谓偏塞者。其意不甚相远矣。然偏塞二字。殊可轻看。盖以上智对下愚。则不能无偏全通塞之可言。而其偏其塞。又非禽兽草木之比耳。以是致疑于变化之工者。恐涉泥滞。原书中亦不能无四字下得极有力。幸更详思。
湖社讲义[二]
安士定问心经人心道心注。西山真氏曰声色臭味之欲。皆发于气。所谓人心也。仁义礼智之理。皆根于性。所谓道心也。人心道心。均是一心。而今直曰人心发于气。道心根于性。则似不无心性二歧之嫌。未知如何。
真氏此说。分明以人心为气。道心为理。来疑云云。盖得之矣。大抵真氏所见。本来如此。故凡论人道。皆有此意。性理大全仁门曰知觉气也。凡能识痛痒识利害者皆是也。自注此所谓人心。又曰若仁义礼智信。则纯是义理。自注曰此所谓道心。于此可见人道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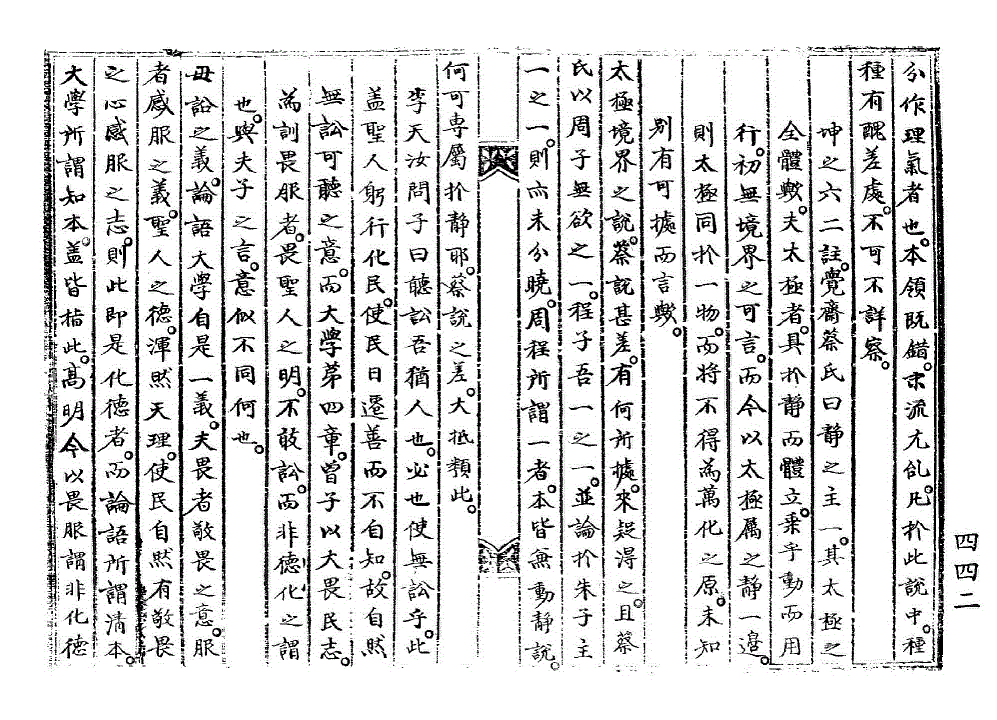 分作理气者也。本领既错。末流尤乱。凡于此说中。种种有丑差处。不可不详察。
分作理气者也。本领既错。末流尤乱。凡于此说中。种种有丑差处。不可不详察。坤之六二注。觉斋蔡氏曰静之主一。其太极之全体欤。夫太极者。具于静而体立。乘乎动而用行。初无境界之可言。而今以太极属之静一边。则太极同于一物。而将不得为万化之原。未知别有可据而言欤。
太极境界之说。蔡说甚差。有何所据。来疑得之。且蔡氏以周子无欲之一。程子吾一之一。并论于朱子主一之一。则亦未分晓。周程所谓一者。本皆兼动静说。何可专属于静耶。蔡说之差。大抵类此。
李天汝问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此盖圣人躬行化民。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自然无讼可听之意。而大学第四章。曾子以大畏民志。为训畏服者。畏圣人之明。不敢讼。而非化德之谓也。与夫子之言。意似不同何也。
毋讼之义。论语大学自是一义。夫畏者敬畏之意。服者感服之义。圣人之德。浑然天理。使民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服之志。则此即是化德者。而论语所谓清本。大学所谓知本。盖皆指此。高明今以畏服谓非化德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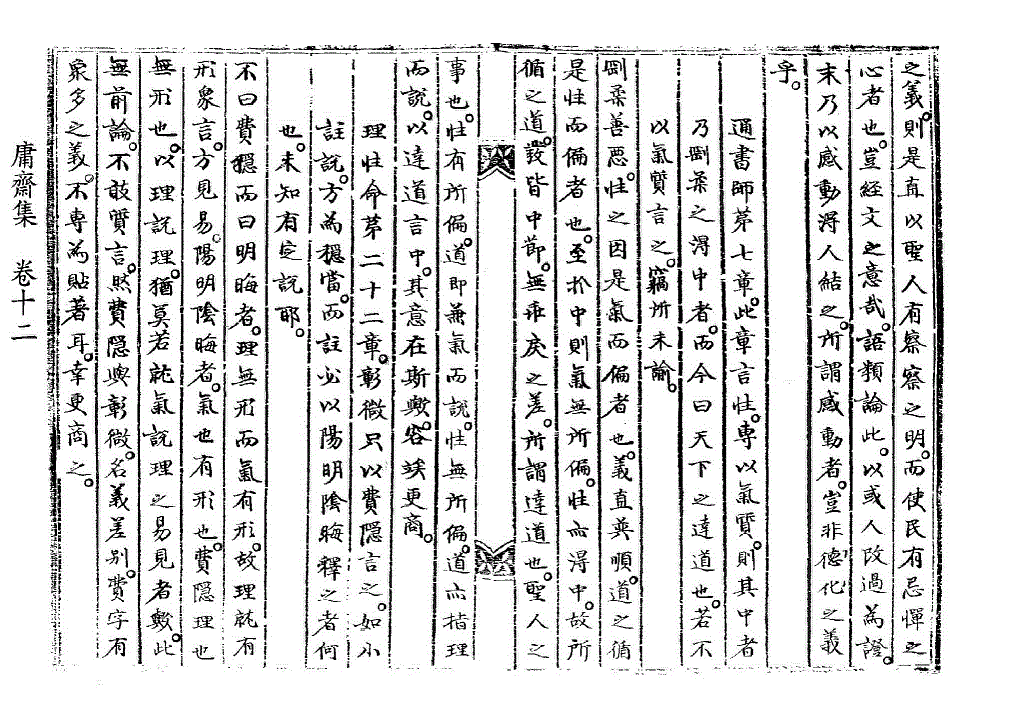 之义。则是直以圣人有察察之明。而使民有忌惮之心者也。岂经文之意哉。语类论此。以或人改过为證。末乃以感动得人结之。所谓感动者。岂非化德之义乎。
之义。则是直以圣人有察察之明。而使民有忌惮之心者也。岂经文之意哉。语类论此。以或人改过为證。末乃以感动得人结之。所谓感动者。岂非化德之义乎。通书师第七章。此章言性。专以气质。则其中者乃刚柔之得中者。而今曰天下之达道也。若不以气质言之。窃所未谕。
刚柔善恶。性之因是气而偏者也。义直巽顺。道之循是性而偏者也。至于中则气无所偏。性亦得中。故所循之道。发皆中节。无乖戾之差。所谓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性有所偏。道即兼气而说。性无所偏。道亦指理而说。以达道言中。其意在斯欤。容俟更商。
理性命第二十二章。彰微只以费隐言之。如小注说。方为稳当。而注必以阳明阴晦释之者何也。未知有定说耶。
不曰费隐而曰明晦者。理无形而气有形。故理就有形象言。方见易。阳明阴晦者。气也有形也。费隐理也无形也。以理说理。犹莫若就气说理之易见者欤。此无前论。不敢质言。然费隐与彰微。名义差别。费字有象多之义。不专为贴著耳。幸更商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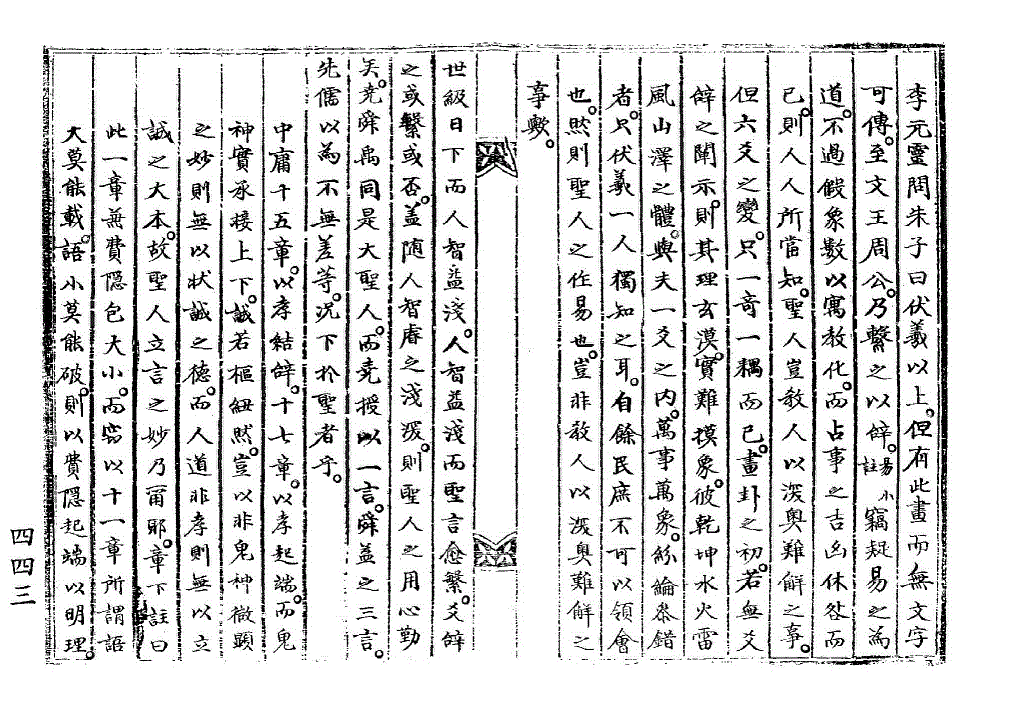 李元灵问朱子曰伏羲以上。但有此画而无文字可传。至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易小注。)窃疑易之为道。不过假象数以寓教化。而占事之吉凶休咎而已。则人人所当知。圣人岂教人以深奥难解之事。但六爻之变。只一奇一耦而已。画卦之初。若无爻辞之阐示。则其理玄漠。实难摸象。彼乾坤水火雷风山泽之体。与夫一爻之内。万事万象。纷纶参错者。只伏羲一人独知之耳。自馀民庶不可以领会也。然则圣人之作易也。岂非教人以深奥难解之事欤。
李元灵问朱子曰伏羲以上。但有此画而无文字可传。至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易小注。)窃疑易之为道。不过假象数以寓教化。而占事之吉凶休咎而已。则人人所当知。圣人岂教人以深奥难解之事。但六爻之变。只一奇一耦而已。画卦之初。若无爻辞之阐示。则其理玄漠。实难摸象。彼乾坤水火雷风山泽之体。与夫一爻之内。万事万象。纷纶参错者。只伏羲一人独知之耳。自馀民庶不可以领会也。然则圣人之作易也。岂非教人以深奥难解之事欤。世级日下而人智益浅。人智益浅而圣言愈繁。爻辞之或繁或否。盖随人智睿之浅深。则圣人之用心勤矣。尧舜禹同是大圣人。而尧授以一言。舜益之三言。先儒以为不无差等。况下于圣者乎。
中庸十五章。以孝结辞。十七章。以孝起端。而鬼神实承接上下。诚若枢纽然。岂以非鬼神微显之妙则无以状诚之德。而人道非孝则无以立诚之大本。故圣人立言之妙乃尔耶。章下注曰此一章兼费隐包大小。而窃以十一章所谓语大莫能载。语小莫能破。则以费隐起端以明理。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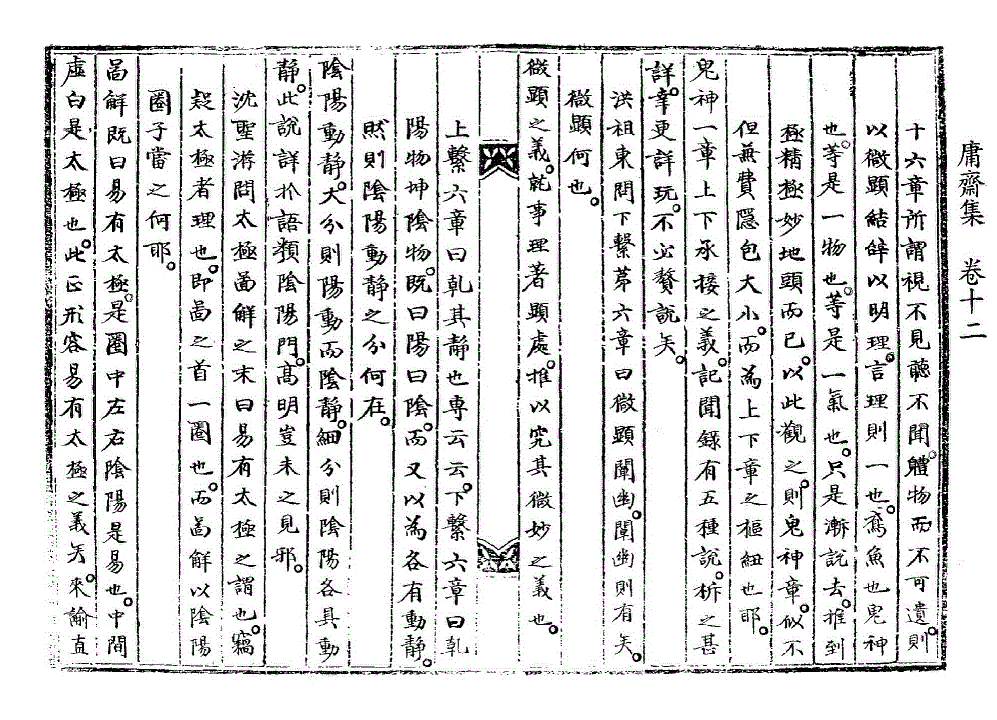 十六章所谓视不见听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则以微显结辞以明理。言理则一也。鸢鱼也鬼神也。等是一物也。等是一气也。只是渐说去。推到极精极妙地头而已。以此观之。则鬼神章。似不但兼费隐包大小。而为上下章之枢纽也耶。
十六章所谓视不见听不闻。体物而不可遗。则以微显结辞以明理。言理则一也。鸢鱼也鬼神也。等是一物也。等是一气也。只是渐说去。推到极精极妙地头而已。以此观之。则鬼神章。似不但兼费隐包大小。而为上下章之枢纽也耶。鬼神一章上下承接之义。记闻录有五种说。析之甚详。幸更详玩。不必赘说矣。
洪祖东问下系第六章曰微显阐幽。阐幽则有矣。微显何也。
微显之义。就事理著显处。推以究其微妙之义也。
上系六章曰乾其静也专云云。下系六章曰乾阳物坤阴物。既曰阳曰阴。而又以为各有动静。然则阴阳动静之分何在。
阴阳动静。大分则阳动而阴静。细分则阴阳各具动静。此说详于语类阴阳门。高明岂未之见邪。
沈圣游问太极啚解之末曰易有太极之谓也。窃疑太极者理也。即啚之首一圈也。而啚解以阴阳圈子当之何耶。
啚解既曰易有太极。是圈中左右阴阳是易也。中间虚白是太极也。此正形容易有太极之义矣。来谕直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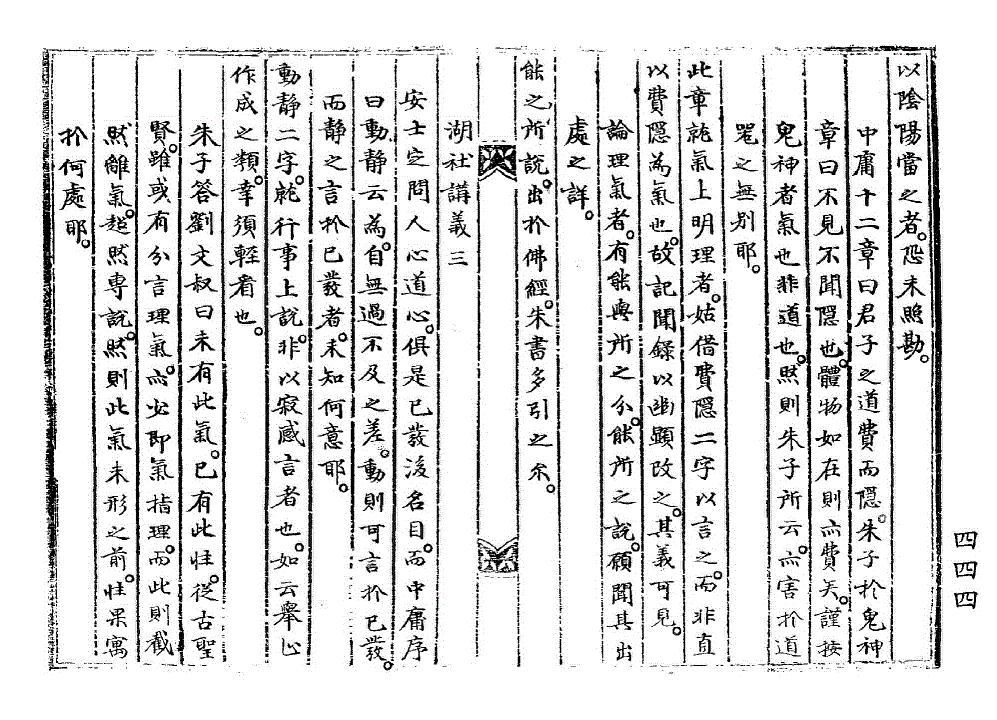 以阴阳当之者。恐未照勘。
以阴阳当之者。恐未照勘。中庸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朱子于鬼神章曰不见不闻隐也。体物如在则亦费矣。谨按鬼神者气也非道也。然则朱子所云。亦害于道器之无别耶。
此章就气上明理者。姑借费隐二字以言之。而非直以费隐为气也。故记闻录以幽显改之。其义可见。
论理气者。有能与所之分。能所之说。愿闻其出处之详。
能之所说。出于佛经。朱书多引之尔。
湖社讲义[三]
安士定问人心道心。俱是已发后名目。而中庸序曰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动则可言于已发。而静之言于已发者。未知何意耶。
动静二字。就行事上说。非以寂感言者也。如云举止作成之类。幸须轻看也。
朱子答刘文叔曰未有此气。已有此性。从古圣贤。虽或有分言理气。亦必即气指理。而此则截然离气。超然专说。然则此气未形之前。性果寓于何处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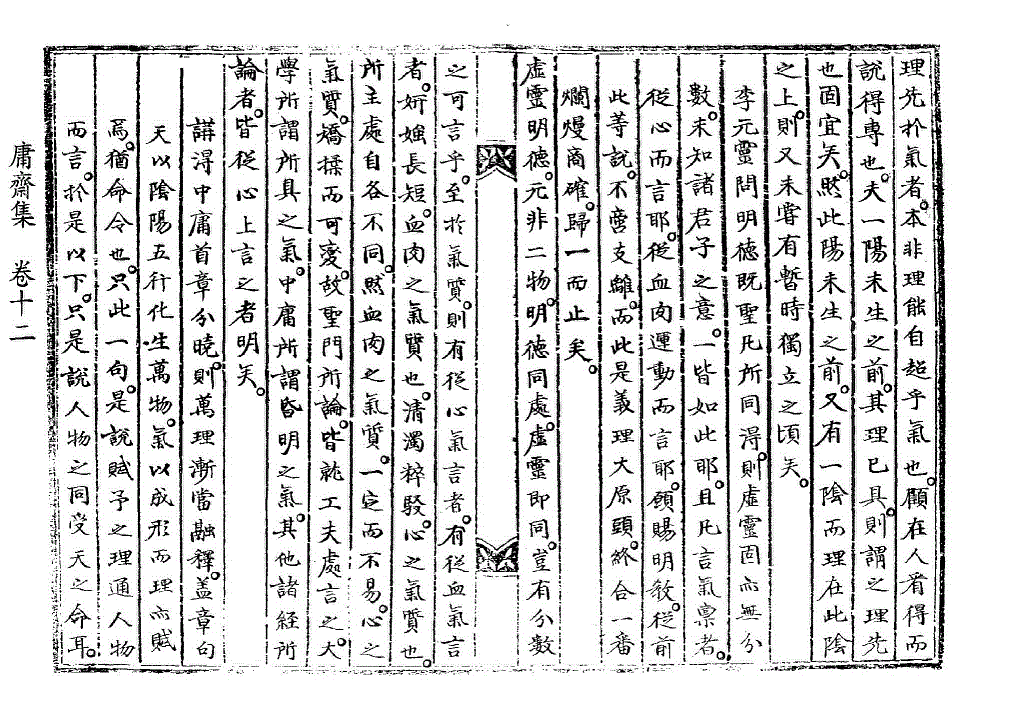 理先于气者。本非理能自超乎气也。顾在人看得而说得专也。夫一阳未生之前。其理已具。则谓之理先也固宜矣。然此阳未生之前。又有一阴而理在此阴之上。则又未尝有暂时独立之顷矣。
理先于气者。本非理能自超乎气也。顾在人看得而说得专也。夫一阳未生之前。其理已具。则谓之理先也固宜矣。然此阳未生之前。又有一阴而理在此阴之上。则又未尝有暂时独立之顷矣。李元灵问明德既圣凡所同得。则虚灵固亦无分数。未知诸君子之意。一皆如此耶。且凡言气禀者。从心而言耶。从血肉运动而言耶。愿赐明教。从前此等说。不啻支离。而此是义理大原头。终合一番烂熳商确。归一而止矣。
虚灵明德。元非二物。明德同处。虚灵即同。岂有分数之可言乎。至于气质。则有从心气言者。有从血气言者。妍媸长短。血肉之气质也。清浊粹驳。心之气质也。所主处自各不同。然血肉之气质。一定而不易。心之气质。矫揉而可变。故圣门所论。皆就工夫处言之。大学所谓所具之气。中庸所谓昏明之气。其他诸经所论者。皆从心上言之者明矣。
讲得中庸首章分晓。则万理渐当融释。盖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只此一句。是说赋予之理通人物而言。于是以下。只是说人物之同受天之命耳。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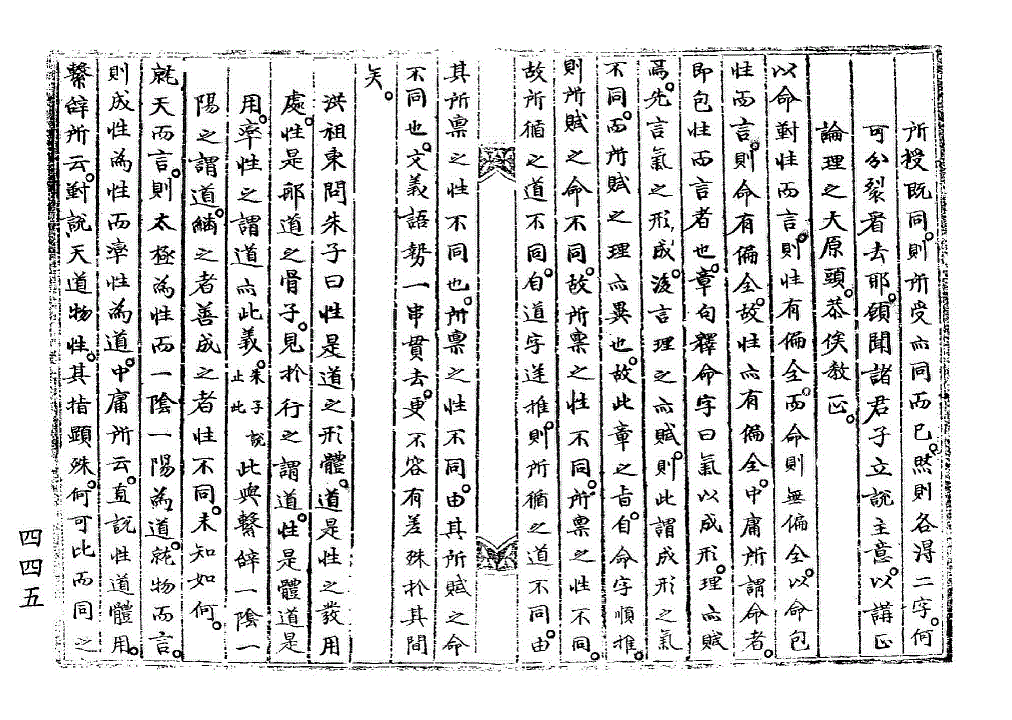 所授既同。则所受亦同而已。然则各得二字。何可分裂看去耶。愿闻诸君子立说主意。以讲正论理之大原头。恭俟教正。
所授既同。则所受亦同而已。然则各得二字。何可分裂看去耶。愿闻诸君子立说主意。以讲正论理之大原头。恭俟教正。以命对性而言。则性有偏全。而命则无偏全。以命包性而言。则命有偏全。故性亦有偏全。中庸所谓命者。即包性而言者也。章句释命字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先言气之成形。后言理之亦赋。则此谓成形之气不同。而所赋之理亦异也。故此章之旨。自命字顺推。则所赋之命不同。故所禀之性不同。所禀之性不同。故所循之道不同。自道字逆推。则所循之道不同。由其所禀之性不同也。所禀之性不同。由其所赋之命不同也。文义语势一串贯去。更不容有差殊于其间矣。
洪祖东问朱子曰性是道之形体。道是性之发用处。性是那道之骨子。见于行之谓道。性是体道是用。率性之谓道亦此义。(朱子说止此)此与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不同。未知如何。
就天而言。则太极为性而一阴一阳为道。就物而言。则成性为性而率性为道。中庸所云。直说性道体用。系辞所云。对说天道物性。其指显殊。何可比而同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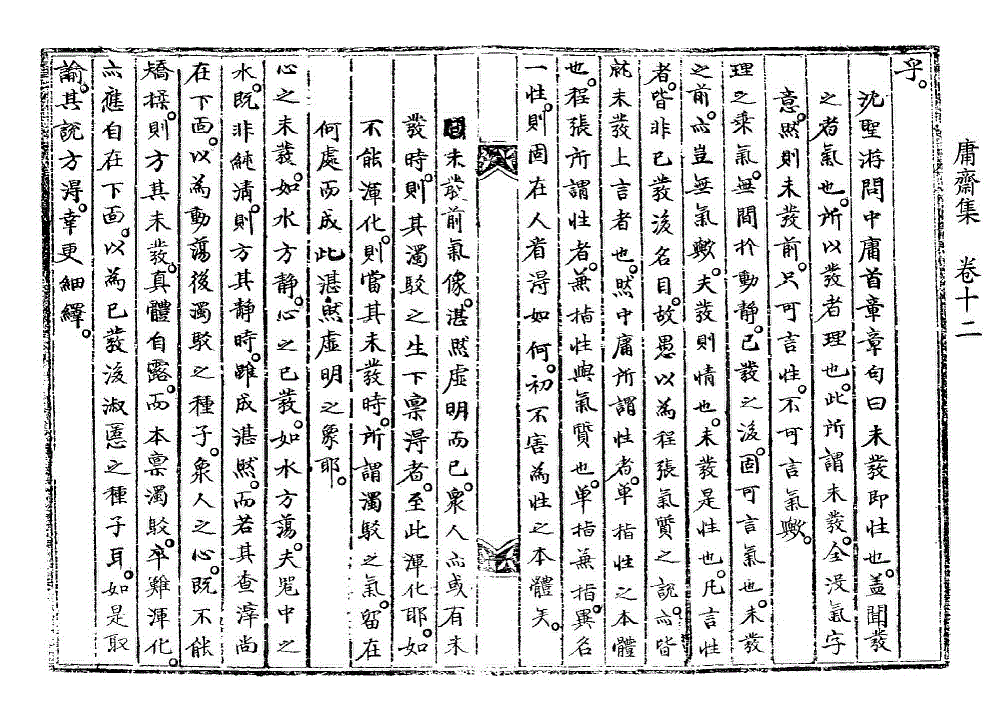 乎。
乎。沈圣游问中庸首章章句曰未发即性也。盖闻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此所谓未发。全没气字意。然则未发前。只可言性。不可言气欤。
理之乘气。无间于动静。已发之后。固可言气也。未发之前。亦岂无气欤。夫发则情也。未发是性也。凡言性者。皆非已发后名目。故愚以为程张气质之说。亦皆就未发上言者也。然中庸所谓性者。单指性之本体也。程张所谓性者。兼指性与气质也。单指兼指。异名一性。则固在人看得如何。初不害为性之本体矣。
未发前气像。湛然虚明而已。众人亦或有未发时。则其浊驳之生下禀得者。至此浑化耶。如不能浑化。则当其未发时。所谓浊驳之气。留在何处而成此湛然虚明之象耶。
心之未发。如水方静。心之已发。如水方荡。夫器中之水。既非纯清。则方其静时。虽成湛然。而若其查滓尚在下面。以为动荡后浊驳之种子。众人之心。既不能矫揉。则方其未发。真体自露。而本禀浊驳。卒难浑化。亦应自在下面。以为已发后淑慝之种子耳。如是取谕。其说方得。幸更细绎。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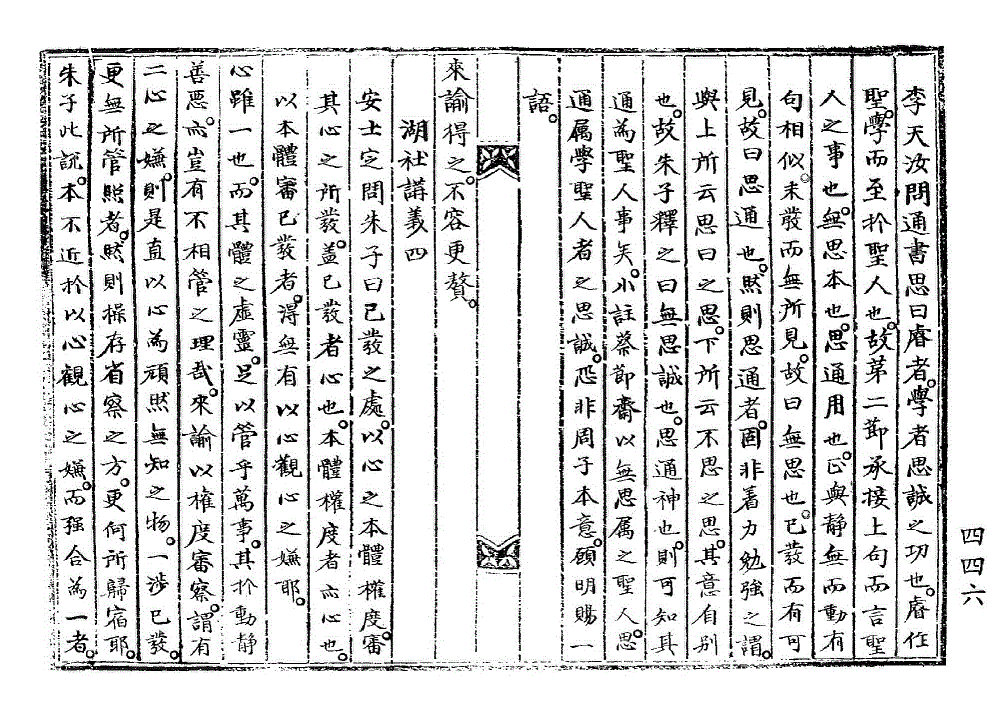 李天汝问通书思曰睿者。学者思诚之功也。睿作圣。学而至于圣人也。故第二节承接上句而言圣人之事也。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正与静无而动有句相似。未发而无所见。故曰无思也。已发而有可见。故曰思通也。然则思通者。固非着力勉强之谓。与上所云思曰之思。下所云不思之思。其意自别也。故朱子释之曰无思诚也。思通神也。则可知其通为圣人事矣。小注蔡节斋以无思属之圣人。思通属学圣人者之思诚。恐非周子本意。愿明赐一语。
李天汝问通书思曰睿者。学者思诚之功也。睿作圣。学而至于圣人也。故第二节承接上句而言圣人之事也。无思本也。思通用也。正与静无而动有句相似。未发而无所见。故曰无思也。已发而有可见。故曰思通也。然则思通者。固非着力勉强之谓。与上所云思曰之思。下所云不思之思。其意自别也。故朱子释之曰无思诚也。思通神也。则可知其通为圣人事矣。小注蔡节斋以无思属之圣人。思通属学圣人者之思诚。恐非周子本意。愿明赐一语。来谕得之。不容更赘。
湖社讲义[四]
安士定问朱子曰已发之处。以心之本体权度。审其心之所发。盖已发者心也。本体权度者亦心也。以本体审已发者。得无有以心观心之嫌耶。
心虽一也。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万事。其于动静善恶。亦岂有不相管之理哉。来谕以权度审察。谓有二心之嫌。则是直以心为顽然无知之物。一涉已发。更无所管照者。然则操存省察之方。更何所归宿耶。朱子此说。本不近于以心观心之嫌。而强合为一者。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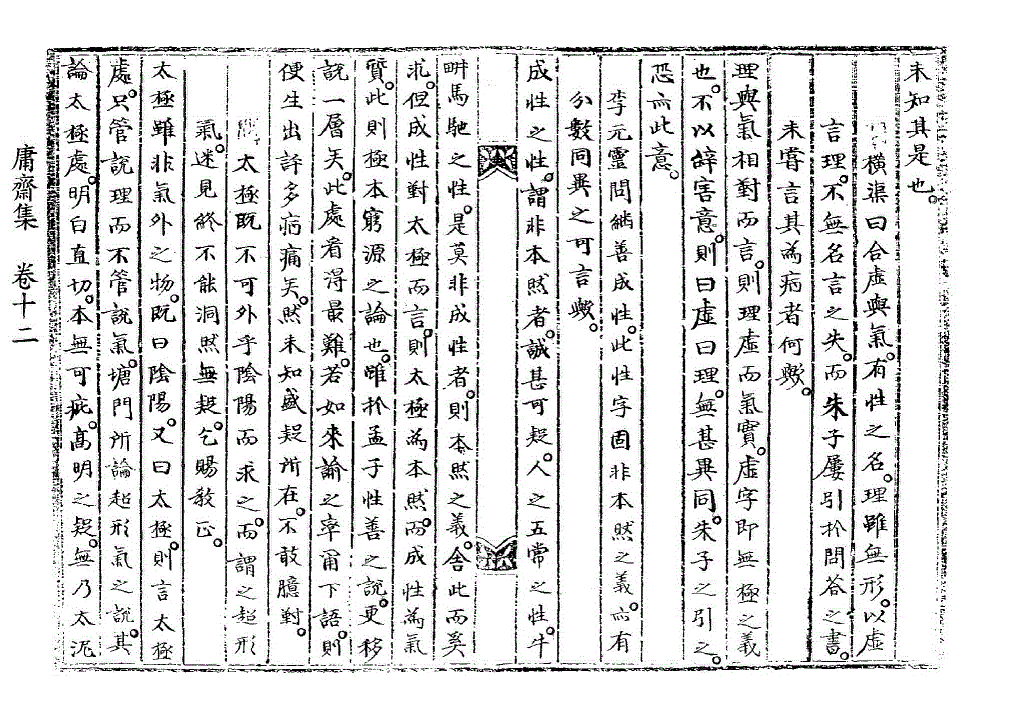 未知其是也。
未知其是也。横渠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理虽无形。以虚言理。不无名言之失。而朱子屡引于问答之书。未尝言其为病者何欤。
理与气相对而言。则理虚而气实。虚字即无极之义也。不以辞害意。则曰虚曰理。无甚异同。朱子之引之。恐亦此意。
李元灵问继善成性。此性字固非本然之义。亦有分数同异之可言欤。
成性之性。谓非本然者。诚甚可疑。人之五常之性。牛耕马驰之性。是莫非成性者。则本然之义。舍此而奚求。但成性对太极而言。则太极为本然。而成性为气质。此则极本穷源之论也。虽于孟子性善之说。更移说一层矣。此处看得最难。若如来谕之率尔下语。则便生出许多病痛矣。然未知盛疑所在。不敢臆对。
太极既不可外乎阴阳而求之。而谓之超形气。迷见终不能洞然无疑。乞赐教正。
太极虽非气外之物。既曰阴阳。又曰太极。则言太极处。只管说理而不管说气。塘门所论超形气之说。其论太极处。明白直切。本无可疵。高明之疑。无乃太泥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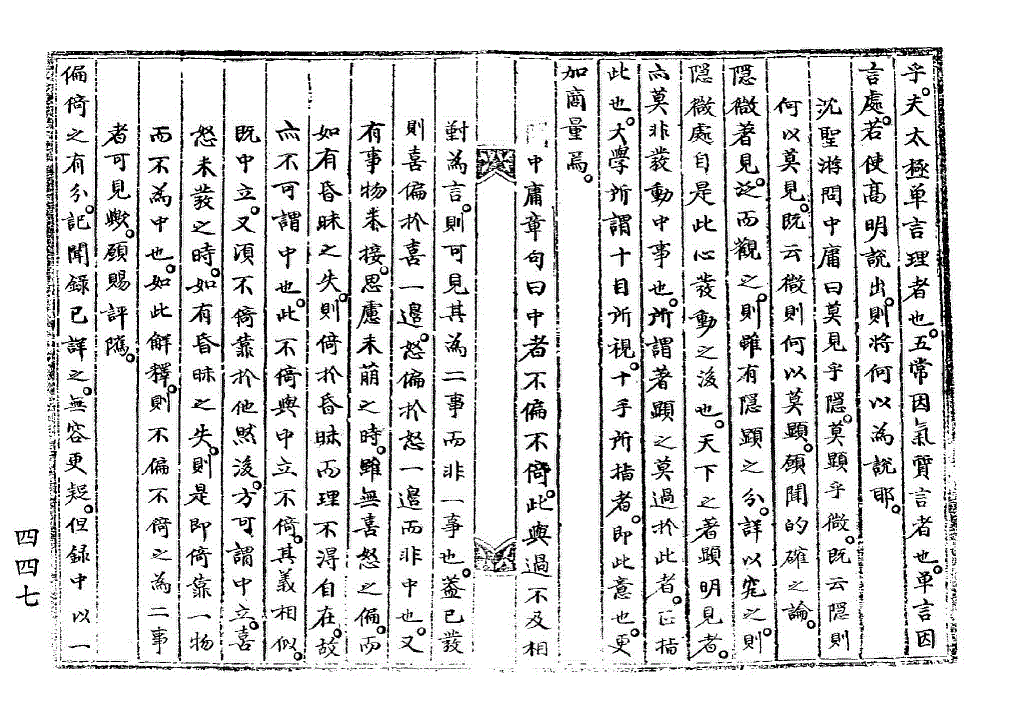 乎。夫太极单言理者也。五常因气质言者也。单言因言处。若使高明说出。则将何以为说耶。
乎。夫太极单言理者也。五常因气质言者也。单言因言处。若使高明说出。则将何以为说耶。沈圣游问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既云隐则何以莫见。既云微则何以莫显。愿闻的确之论。
隐微著见。泛而观之。则虽有隐显之分。详以究之。则隐微处自是此心发动之后也。天下之著显明见者。亦莫非发动中事也。所谓著显之莫过于此者。正指此也。大学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者。即此意也。更加商量焉。
中庸章句曰中者不偏不倚。此与过不及相对为言。则可见其为二事而非一事也。盖已发则喜偏于喜一边。怒偏于怒一边而非中也。又有事物未接。思虑未萌之时。虽无喜怒之偏。而如有昏昧之失。则倚于昏昧而理不得自在。故亦不可谓中也。此不倚与中立不倚。其义相似。既中立。又须不倚靠于他然后。方可谓中立。喜怒未发之时。如有昏昧之失。则是即倚靠一物而不为中也。如此解释。则不偏不倚之为二事者可见欤。愿赐评骘。
偏倚之有分。记闻录已详之。无容更疑。但录中以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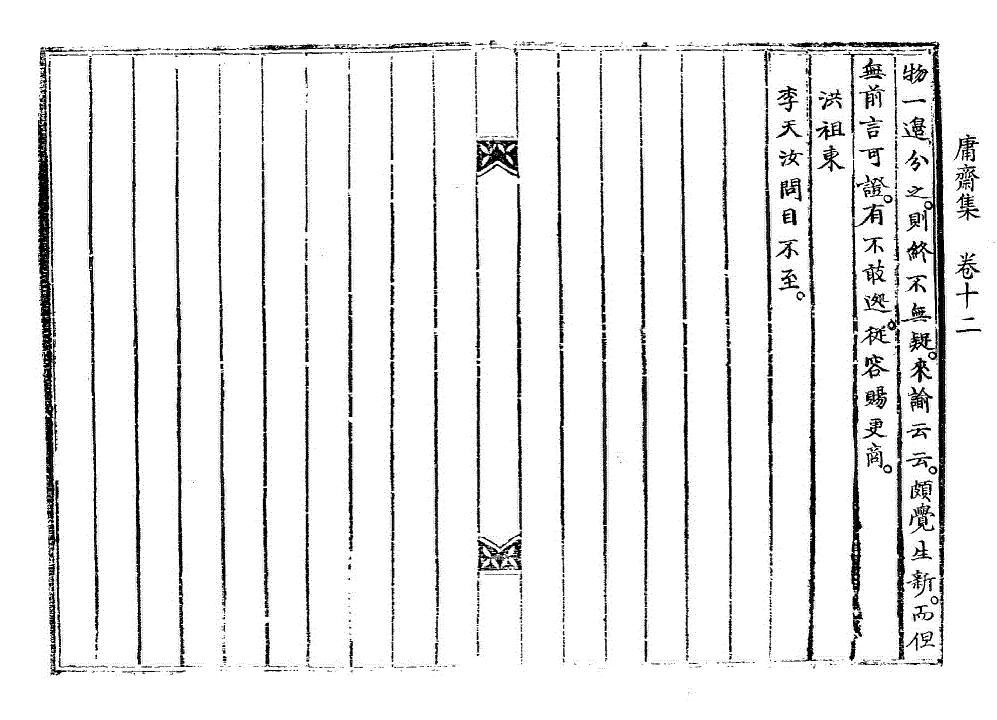 物一边分之。则终不无疑。来谕云云。颇觉生新。而但无前言可證。有不敢遽。从容赐更商。
物一边分之。则终不无疑。来谕云云。颇觉生新。而但无前言可證。有不敢遽。从容赐更商。洪祖东
李天汝问目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