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书
书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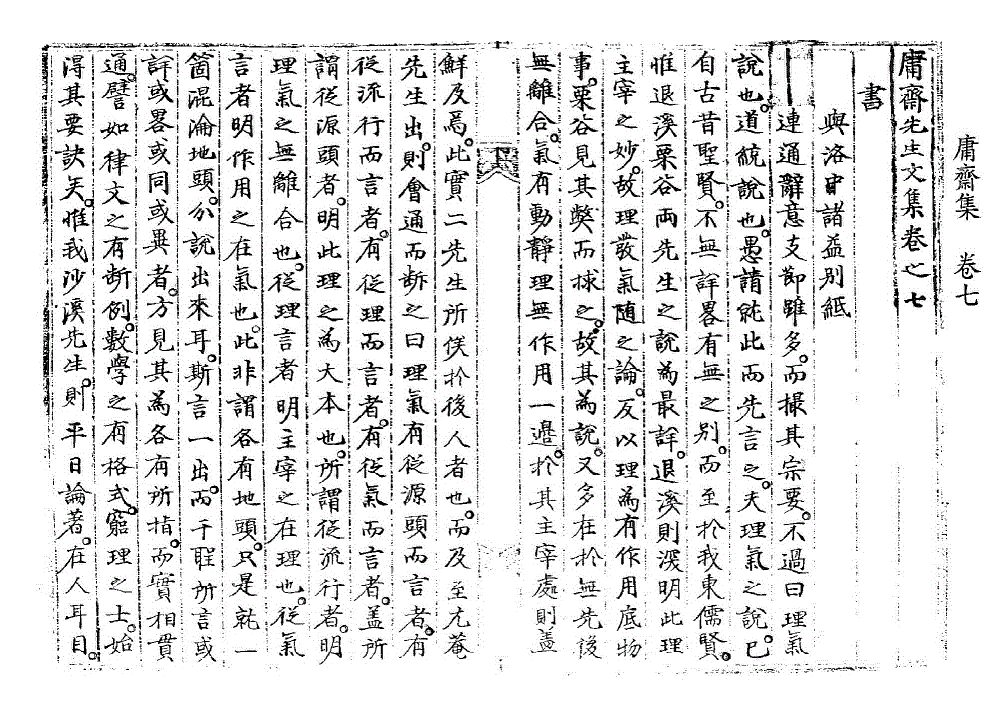 与洛中诸益别纸
与洛中诸益别纸连通辞意支节虽多。而撮其宗要。不过曰理气说也。道统说也。愚请就此而先言之。夫理气之说。已自古昔圣贤。不无详略有无之别。而至于我东儒贤。惟退溪栗谷两先生之说为最详。退溪则深明此理主宰之妙。故理发气随之论。反以理为有作用底物事。栗谷见其弊而救之。故其为说。又多在于无先后无离合。气有动静理无作用一边。于其主宰处则盖鲜及焉。此实二先生所俟于后人者也。而及至尤庵先生出。则会通而断之曰理气有从源头而言者。有从流行而言者。有从理而言者。有从气而言者。盖所谓从源头者。明此理之为大本也。所谓从流行者。明理气之无离合也。从理言者明主宰之在理也。从气言者明作用之在气也。此非谓各有地头。只是就一个混沦地头。分说出来耳。斯言一出。而千圣所言或详或略或同或异者。方见其为各有所指。而实相贯通。譬如律文之有断例。数学之有格式。穷理之士。始得其要诀矣。惟我沙溪先生。则平日论著。在人耳目。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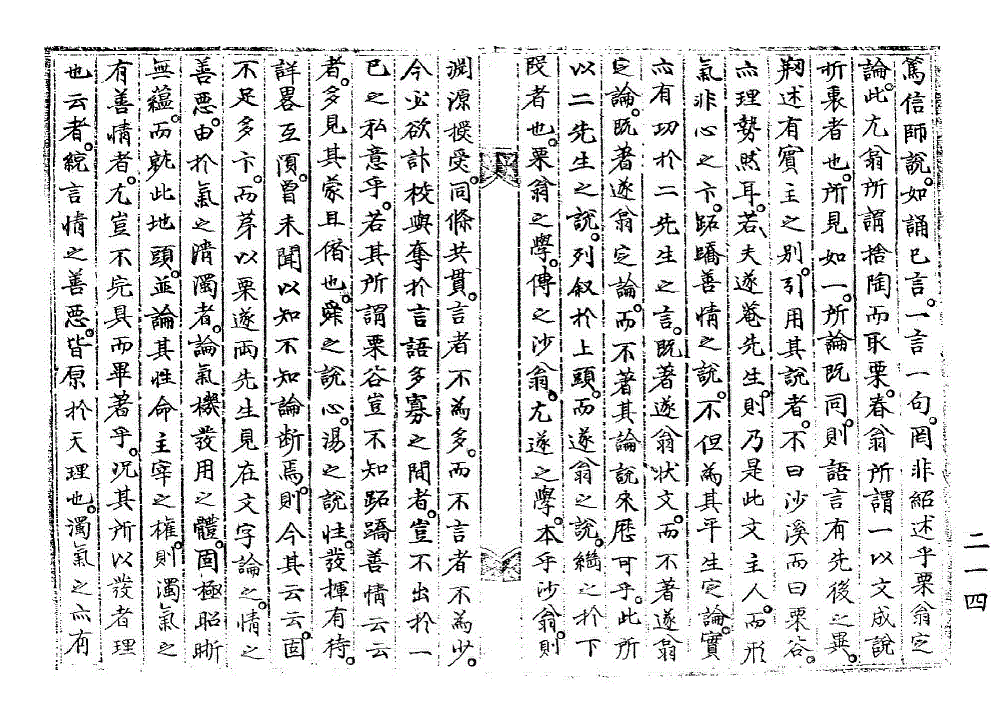 笃信师说。如诵己言。一言一句。罔非绍述乎栗翁定论。此尤翁所谓舍陶而取栗。春翁所谓一以文成说折衷者也。所见如一。所论既同。则语言有先后之异。刱述有宾主之别。引用其说者。不曰沙溪而曰栗谷。亦理势然耳。若夫遂庵先生。则乃是此文主人。而形气非心之卞。蹠蹻善情之说。不但为其平生定论。实亦有功于二先生之言。既著遂翁状文。而不著遂翁定论。既著遂翁定论。而不著其论说来历可乎。此所以二先生之说。列叙于上头。而遂翁之说。继之于下段者也。栗翁之学。传之沙翁。尤遂之学。本乎沙翁。则渊源授受。同条共贯。言者不为多。而不言者不为少。今必欲计校与夺于言语多寡之间者。岂不出于一己之私意乎。若其所谓栗谷岂不知蹠蹻善情云云者。多见其蒙且僭也。舜之说心。汤之说性。发挥有待。详略互须。曾未闻以知不知论断焉。则今其云云。固不足多卞。而第以栗遂两先生见在文字论之。情之善恶。由于气之清浊者。论气机发用之体。固极昭晢无蕴。而就此地头。并论其性命主宰之权。则浊气之有善情者。尤岂不完具而毕著乎。况其所以发者理也云者。统言情之善恶。皆原于天理也。浊气之亦有
笃信师说。如诵己言。一言一句。罔非绍述乎栗翁定论。此尤翁所谓舍陶而取栗。春翁所谓一以文成说折衷者也。所见如一。所论既同。则语言有先后之异。刱述有宾主之别。引用其说者。不曰沙溪而曰栗谷。亦理势然耳。若夫遂庵先生。则乃是此文主人。而形气非心之卞。蹠蹻善情之说。不但为其平生定论。实亦有功于二先生之言。既著遂翁状文。而不著遂翁定论。既著遂翁定论。而不著其论说来历可乎。此所以二先生之说。列叙于上头。而遂翁之说。继之于下段者也。栗翁之学。传之沙翁。尤遂之学。本乎沙翁。则渊源授受。同条共贯。言者不为多。而不言者不为少。今必欲计校与夺于言语多寡之间者。岂不出于一己之私意乎。若其所谓栗谷岂不知蹠蹻善情云云者。多见其蒙且僭也。舜之说心。汤之说性。发挥有待。详略互须。曾未闻以知不知论断焉。则今其云云。固不足多卞。而第以栗遂两先生见在文字论之。情之善恶。由于气之清浊者。论气机发用之体。固极昭晢无蕴。而就此地头。并论其性命主宰之权。则浊气之有善情者。尤岂不完具而毕著乎。况其所以发者理也云者。统言情之善恶。皆原于天理也。浊气之亦有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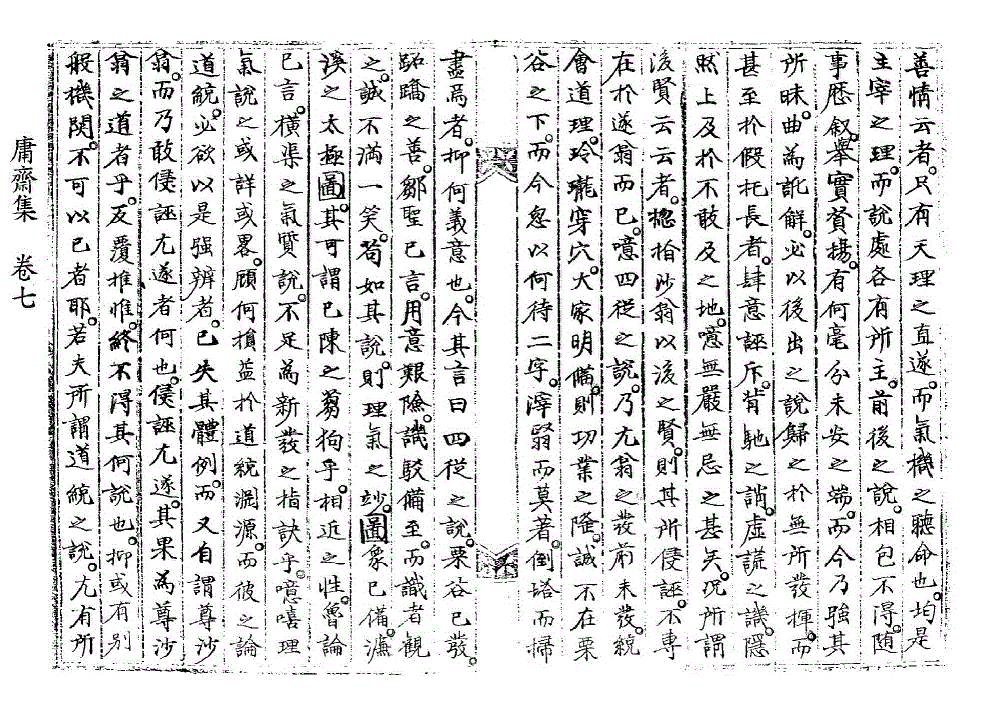 善情云者。只有天理之直遂。而气机之听命也。均是主宰之理。而说处各有所主。前后之说。相包不得。随事历叙。举实赞扬。有何毫分未安之端。而今乃强其所昧。曲为讹解。必以后出之说归之于无所发挥。而甚至于假托长者。肆意诬斥。背驰之诮。虚谎之讥。隐然上及于不敢及之地。噫无严无忌之甚矣。况所谓后贤云云者。揔指沙翁以后之贤。则其所侵诬。不专在于遂翁而已。噫四从之说。乃尤翁之发前未发。统会道理。玲珑穿穴。大家明备。则功业之隆。诚不在栗谷之下。而今忽以何待二字。滓翳而莫著。倒塔而扫尽焉者。抑何义意也。今其言曰四从之说。栗谷已发。蹠蹻之善。邹圣已言。用意艰险。讥驳备至。而识者观之。诚不满一笑。苟如其说。则理气之妙。图象已备。濂溪之太极图。其可谓已陈之刍狗乎。相近之性。鲁论已言。横渠之气质说。不足为新发之指诀乎。噫嘻理气说之或详或略。顾何损益于道统渊源。而彼之论道统。必欲以是强辨者。已失其体例。而又自谓尊沙翁。而乃敢侵诬尤遂者何也。侵诬尤遂。其果为尊沙翁之道者乎。反覆推惟。终不得其何说也。抑或有别般机关。不可以已者耶。若夫所谓道统之说。尤有所
善情云者。只有天理之直遂。而气机之听命也。均是主宰之理。而说处各有所主。前后之说。相包不得。随事历叙。举实赞扬。有何毫分未安之端。而今乃强其所昧。曲为讹解。必以后出之说归之于无所发挥。而甚至于假托长者。肆意诬斥。背驰之诮。虚谎之讥。隐然上及于不敢及之地。噫无严无忌之甚矣。况所谓后贤云云者。揔指沙翁以后之贤。则其所侵诬。不专在于遂翁而已。噫四从之说。乃尤翁之发前未发。统会道理。玲珑穿穴。大家明备。则功业之隆。诚不在栗谷之下。而今忽以何待二字。滓翳而莫著。倒塔而扫尽焉者。抑何义意也。今其言曰四从之说。栗谷已发。蹠蹻之善。邹圣已言。用意艰险。讥驳备至。而识者观之。诚不满一笑。苟如其说。则理气之妙。图象已备。濂溪之太极图。其可谓已陈之刍狗乎。相近之性。鲁论已言。横渠之气质说。不足为新发之指诀乎。噫嘻理气说之或详或略。顾何损益于道统渊源。而彼之论道统。必欲以是强辨者。已失其体例。而又自谓尊沙翁。而乃敢侵诬尤遂者何也。侵诬尤遂。其果为尊沙翁之道者乎。反覆推惟。终不得其何说也。抑或有别般机关。不可以已者耶。若夫所谓道统之说。尤有所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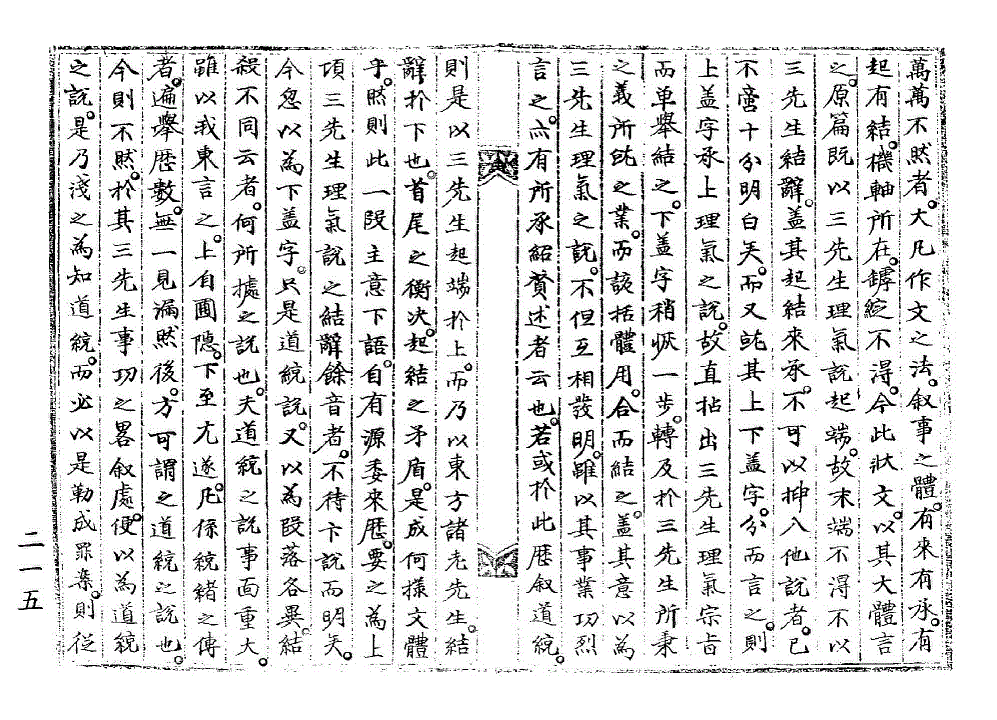 万万不然者。大凡作文之法。叙事之体。有来有承。有起有结。机轴所在。罅绽不得。今此状文。以其大体言之。原篇既以三先生理气说起端。故末端不得不以三先生结辞。盖其起结来承。不可以插入他说者。已不啻十分明白矣。而又就其上下盖字。分而言之。则上盖字承上理气之说。故直拈出三先生理气宗旨而单举结之。下盖字稍恢一步。转及于三先生所秉之义所就之业。而该括体用。合而结之。盖其意以为三先生理气之说。不但互相发明。虽以其事业功烈言之。亦有所承绍赞述者云也。若或于此历叙道统。则是以三先生起端于上。而乃以东方诸老先生。结辞于下也。首尾之衡决。起结之矛盾。是成何㨾文体乎。然则此一段主意下语。自有源委来历。要之为上项三先生理气说之结辞馀音者。不待卞说而明矣。今忽以为下盖字。只是道统说。又以为段落各异。结杀不同云者。何所据之说也。夫道统之说事面重大。虽以我东言之。上自圃隐。下至尤遂。凡系统绪之传者。遍举历数。无一见漏然后。方可谓之道统之说也。今则不然。于其三先生事功之略叙处。便以为道统之说。是乃浅之为知道统。而必以是勒成罪案。则从
万万不然者。大凡作文之法。叙事之体。有来有承。有起有结。机轴所在。罅绽不得。今此状文。以其大体言之。原篇既以三先生理气说起端。故末端不得不以三先生结辞。盖其起结来承。不可以插入他说者。已不啻十分明白矣。而又就其上下盖字。分而言之。则上盖字承上理气之说。故直拈出三先生理气宗旨而单举结之。下盖字稍恢一步。转及于三先生所秉之义所就之业。而该括体用。合而结之。盖其意以为三先生理气之说。不但互相发明。虽以其事业功烈言之。亦有所承绍赞述者云也。若或于此历叙道统。则是以三先生起端于上。而乃以东方诸老先生。结辞于下也。首尾之衡决。起结之矛盾。是成何㨾文体乎。然则此一段主意下语。自有源委来历。要之为上项三先生理气说之结辞馀音者。不待卞说而明矣。今忽以为下盖字。只是道统说。又以为段落各异。结杀不同云者。何所据之说也。夫道统之说事面重大。虽以我东言之。上自圃隐。下至尤遂。凡系统绪之传者。遍举历数。无一见漏然后。方可谓之道统之说也。今则不然。于其三先生事功之略叙处。便以为道统之说。是乃浅之为知道统。而必以是勒成罪案。则从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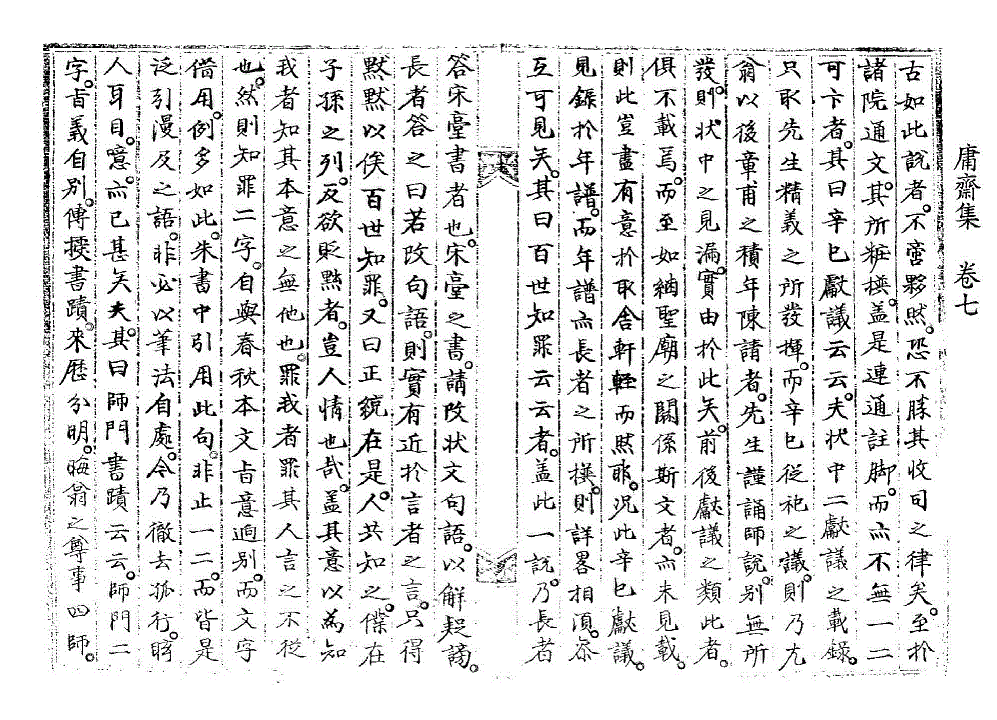 古如此说者。不啻夥然。恐不胜其收司之律矣。至于诸院通文。其所妆撰。盖是连通注脚。而亦不无一二可卞者。其曰辛巳献议云云。夫状中二献议之载录。只取先生精义之所发挥。而辛巳从祀之议。则乃尤翁以后章甫之积年陈请者。先生谨诵师说。别无所发。则状中之见漏。实由于此矣。前后献议之类此者。俱不载焉。而至如继圣庙之关系斯文者。亦未见载。则此岂尽有意于取舍轩轾而然耶。况此辛巳献议。见录于年谱。而年谱亦长者之所撰。则详略相须。参互可见矣。其曰百世知罪云云者。盖此一说。乃长者答宋台书者也。宋台之书。请改状文句语。以解疑谤。长者答之曰若改句语。则实有近于言者之言。只得默默以俟百世知罪。又曰正统在是。人共知之。仆在子孙之列。反欲贬黜者。岂人情也哉。盖其意以为知我者知其本意之无他也。罪我者罪其人言之不从也。然则知罪二字。自与春秋本文旨意迥别。而文字借用。例多如此。朱书中引用此句。非止一二。而皆是泛引漫及之语。非必以笔法自处。今乃彻去孤行。眩人耳目。噫。亦已甚矣夫。其曰师门书迹云云。师门二字。旨义自别。传授书迹。来历分明。晦翁之尊事四师。
古如此说者。不啻夥然。恐不胜其收司之律矣。至于诸院通文。其所妆撰。盖是连通注脚。而亦不无一二可卞者。其曰辛巳献议云云。夫状中二献议之载录。只取先生精义之所发挥。而辛巳从祀之议。则乃尤翁以后章甫之积年陈请者。先生谨诵师说。别无所发。则状中之见漏。实由于此矣。前后献议之类此者。俱不载焉。而至如继圣庙之关系斯文者。亦未见载。则此岂尽有意于取舍轩轾而然耶。况此辛巳献议。见录于年谱。而年谱亦长者之所撰。则详略相须。参互可见矣。其曰百世知罪云云者。盖此一说。乃长者答宋台书者也。宋台之书。请改状文句语。以解疑谤。长者答之曰若改句语。则实有近于言者之言。只得默默以俟百世知罪。又曰正统在是。人共知之。仆在子孙之列。反欲贬黜者。岂人情也哉。盖其意以为知我者知其本意之无他也。罪我者罪其人言之不从也。然则知罪二字。自与春秋本文旨意迥别。而文字借用。例多如此。朱书中引用此句。非止一二。而皆是泛引漫及之语。非必以笔法自处。今乃彻去孤行。眩人耳目。噫。亦已甚矣夫。其曰师门书迹云云。师门二字。旨义自别。传授书迹。来历分明。晦翁之尊事四师。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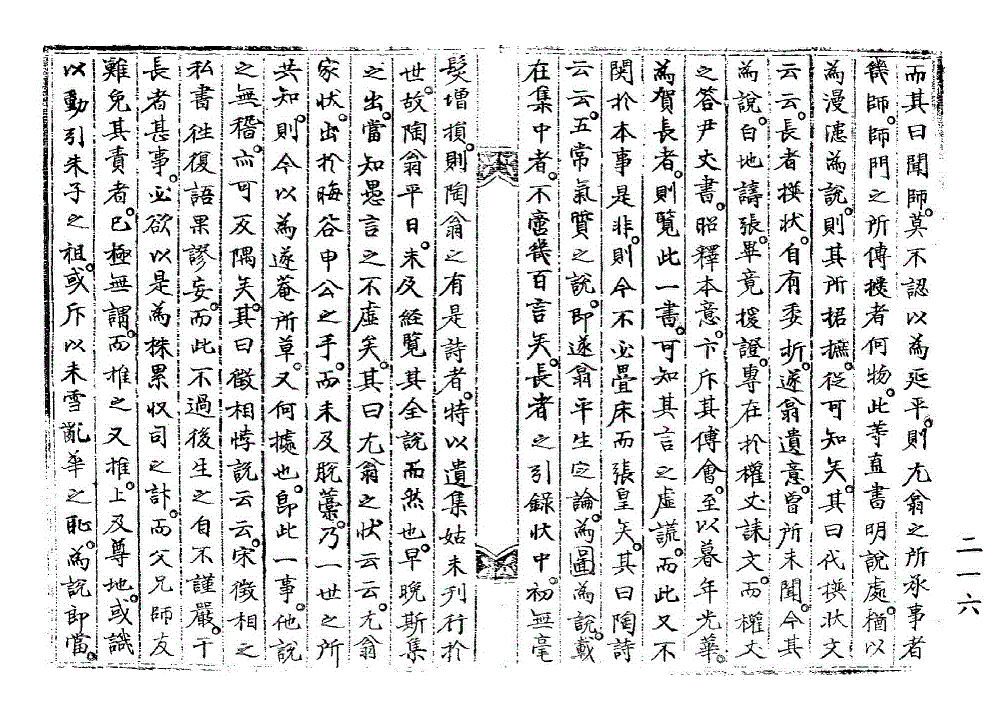 而其曰闻师。莫不认以为延平。则尤翁之所承事者几师。师门之所传授者何物。此等直书明说处。犹以为漫漶为说。则其所捃摭。从可知矣。其曰代撰状文云云。长者撰状。自有委折。遂翁遗意。曾所未闻。今其为说。白地诪张。毕竟援證。专在于权丈诔文。而权丈之答尹丈书。昭释本意。卞斥其傅会。至以暮年光华。为贺长者。则览此一书。可知其言之虚谎。而此又不关于本事是非。则今不必叠床而张皇矣。其曰陶诗云云。五常气质之说。即遂翁平生定论。为图为说。载在集中者。不啻几百言矣。长者之引录状中。初无毫发增损。则陶翁之有是诗者。特以遗集姑未刊行于世。故陶翁平日。未及经览其全说而然也。早晚斯集之出。当知愚言之不虚矣。其曰尤翁之状云云。尤翁家状。出于晦谷申公之手。而未及脱藁。乃一世之所共知。则今以为遂庵所草。又何据也。即此一事。他说之无稽。亦可反隅矣。其曰徵相悖说云云。宋徵相之私书往复语果谬妄。而此不过后生之自不谨严。干长者甚事。必欲以是为株累收司之计。而父兄师友难免其责者。已极无谓。而推之又推。上及尊地。或讥以动引朱子之祖。或斥以未雪乱华之耻。为说郎当。
而其曰闻师。莫不认以为延平。则尤翁之所承事者几师。师门之所传授者何物。此等直书明说处。犹以为漫漶为说。则其所捃摭。从可知矣。其曰代撰状文云云。长者撰状。自有委折。遂翁遗意。曾所未闻。今其为说。白地诪张。毕竟援證。专在于权丈诔文。而权丈之答尹丈书。昭释本意。卞斥其傅会。至以暮年光华。为贺长者。则览此一书。可知其言之虚谎。而此又不关于本事是非。则今不必叠床而张皇矣。其曰陶诗云云。五常气质之说。即遂翁平生定论。为图为说。载在集中者。不啻几百言矣。长者之引录状中。初无毫发增损。则陶翁之有是诗者。特以遗集姑未刊行于世。故陶翁平日。未及经览其全说而然也。早晚斯集之出。当知愚言之不虚矣。其曰尤翁之状云云。尤翁家状。出于晦谷申公之手。而未及脱藁。乃一世之所共知。则今以为遂庵所草。又何据也。即此一事。他说之无稽。亦可反隅矣。其曰徵相悖说云云。宋徵相之私书往复语果谬妄。而此不过后生之自不谨严。干长者甚事。必欲以是为株累收司之计。而父兄师友难免其责者。已极无谓。而推之又推。上及尊地。或讥以动引朱子之祖。或斥以未雪乱华之耻。为说郎当。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7H 页
 不少顾忌。而至于必华悖通。则若其争是非以下三十五字。全袭尼尹诬辱大老之悖语。读未终篇。令人臆塞。噫嘻此何事哉。盖此状文旨意明白。本不难晓。稍通文理者。便可识解。则彼岂全昧于理气道统之分。答问叙事之体也。诚以不如是。无以加贬损之目故耳。然其一世不可诬。则其所以锻鍊深文者。徒归于自欺欺人之科矣。呜呼。惟我沙溪先生道德崇深。知行全备。亲传亲授。式前焘后。至于晚年典礼之功。实启东方秩叙之文。其所以羽翼斯道。上接乎濂闽的源者。不但有先辈定论。亦将俟百世而不惑。凡今之人。孰敢异议于是哉。况我函丈。本以先生之弥甥。亲炙遂翁之门。则是岂自绝其根本。甘心为诬悖者哉。是以顷年承召入京也。入而登筵则历陈东方道德之传。出而陈疏则抄选传道圣贤之言。辄举沙溪先生。以明传授之次第渊源之正脉。其与知旧门人往复问答。凡论沙翁之统绪与从享者。又不啻累百言矣。虽以所撰遂翁行状观之。其于立纲叙事处。特书沙翁之正统嫡传者。已是大煞明白矣。其下总论。虽专以三先生理气说为主。而亦不敢全没道统之意。于其末段结辞。提出道东最著四字。包尽圃隐以
不少顾忌。而至于必华悖通。则若其争是非以下三十五字。全袭尼尹诬辱大老之悖语。读未终篇。令人臆塞。噫嘻此何事哉。盖此状文旨意明白。本不难晓。稍通文理者。便可识解。则彼岂全昧于理气道统之分。答问叙事之体也。诚以不如是。无以加贬损之目故耳。然其一世不可诬。则其所以锻鍊深文者。徒归于自欺欺人之科矣。呜呼。惟我沙溪先生道德崇深。知行全备。亲传亲授。式前焘后。至于晚年典礼之功。实启东方秩叙之文。其所以羽翼斯道。上接乎濂闽的源者。不但有先辈定论。亦将俟百世而不惑。凡今之人。孰敢异议于是哉。况我函丈。本以先生之弥甥。亲炙遂翁之门。则是岂自绝其根本。甘心为诬悖者哉。是以顷年承召入京也。入而登筵则历陈东方道德之传。出而陈疏则抄选传道圣贤之言。辄举沙溪先生。以明传授之次第渊源之正脉。其与知旧门人往复问答。凡论沙翁之统绪与从享者。又不啻累百言矣。虽以所撰遂翁行状观之。其于立纲叙事处。特书沙翁之正统嫡传者。已是大煞明白矣。其下总论。虽专以三先生理气说为主。而亦不敢全没道统之意。于其末段结辞。提出道东最著四字。包尽圃隐以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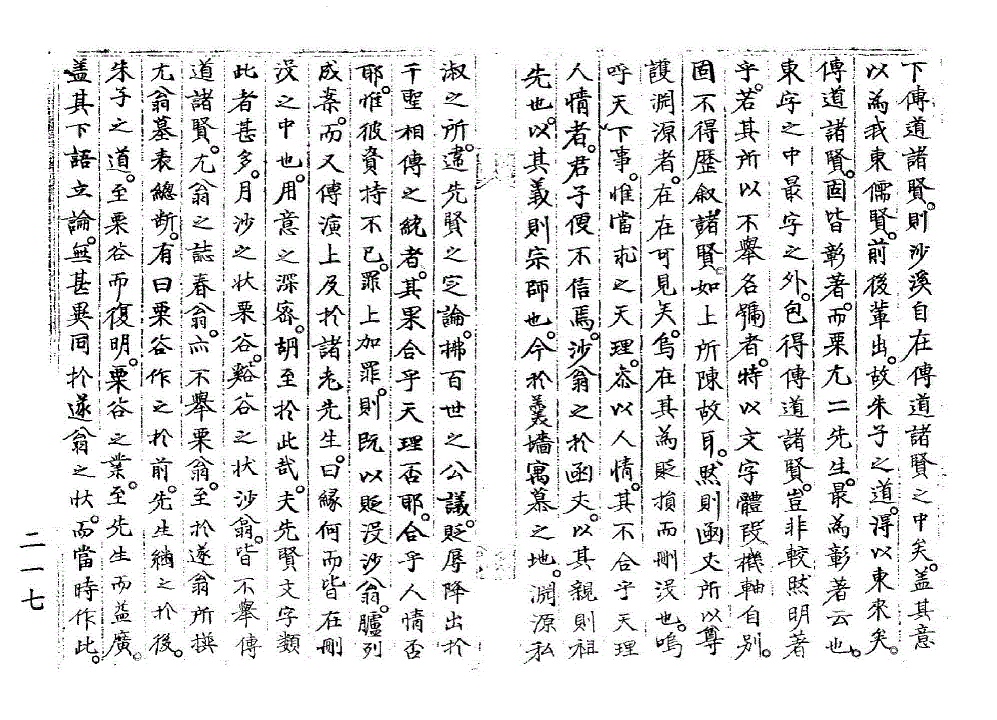 下传道诸贤。则沙溪自在传道诸贤之中矣。盖其意以为我东儒贤。前后辈出。故朱子之道。得以东来矣。传道诸贤。固皆彰著。而栗尤二先生。最为彰著云也。东字之中最字之外。包得传道诸贤。岂非较然明著乎。若其所以不举名号者。特以文字体段机轴自别。固不得历叙诸贤。如上所陈故耳。然则函丈所以尊护渊源者。在在可见矣。乌在其为贬损而删没也。呜呼天下事。惟当求之天理。参以人情。其不合乎天理人情者。君子便不信焉。沙翁之于函丈。以其亲则祖先也。以其义则宗师也。今于羹墙寓慕之地。渊源私淑之所。违先贤之定论。拂百世之公议。贬辱降出于千圣相传之统者。其果合乎天理否耶。合乎人情否耶。惟彼䝱持不已。罪上加罪。则既以贬没沙翁。胪列成案。而又傅演上及于诸老先生。曰缘何而皆在删没之中也。用意之深密。胡至于此哉。夫先贤文字类此者甚多。月沙之状栗谷。溪谷之状沙翁。皆不举传道诸贤。尤翁之志春翁。亦不举栗翁。至于遂翁所撰尤翁墓表总断。有曰栗谷作之于前。先生继之于后。朱子之道。至栗谷而复明。栗谷之业。至先生而益广。盖其下语立论。无甚异同于遂翁之状。而当时作此。
下传道诸贤。则沙溪自在传道诸贤之中矣。盖其意以为我东儒贤。前后辈出。故朱子之道。得以东来矣。传道诸贤。固皆彰著。而栗尤二先生。最为彰著云也。东字之中最字之外。包得传道诸贤。岂非较然明著乎。若其所以不举名号者。特以文字体段机轴自别。固不得历叙诸贤。如上所陈故耳。然则函丈所以尊护渊源者。在在可见矣。乌在其为贬损而删没也。呜呼天下事。惟当求之天理。参以人情。其不合乎天理人情者。君子便不信焉。沙翁之于函丈。以其亲则祖先也。以其义则宗师也。今于羹墙寓慕之地。渊源私淑之所。违先贤之定论。拂百世之公议。贬辱降出于千圣相传之统者。其果合乎天理否耶。合乎人情否耶。惟彼䝱持不已。罪上加罪。则既以贬没沙翁。胪列成案。而又傅演上及于诸老先生。曰缘何而皆在删没之中也。用意之深密。胡至于此哉。夫先贤文字类此者甚多。月沙之状栗谷。溪谷之状沙翁。皆不举传道诸贤。尤翁之志春翁。亦不举栗翁。至于遂翁所撰尤翁墓表总断。有曰栗谷作之于前。先生继之于后。朱子之道。至栗谷而复明。栗谷之业。至先生而益广。盖其下语立论。无甚异同于遂翁之状。而当时作此。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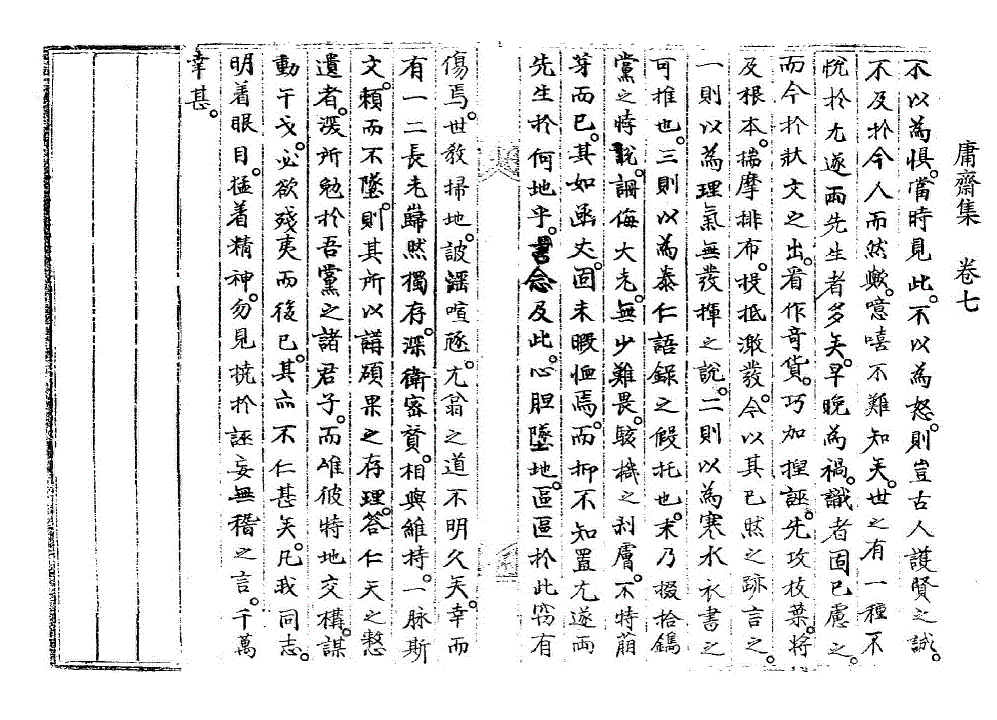 不以为惧。当时见此。不以为怒。则岂古人护贤之诚。不及于今人而然欤。噫嘻不难知矣。世之有一种不悦于尤遂两先生者多矣。早晚为祸。识者固已虑之。而今于状文之出。看作奇货。巧加捏诬。先攻枝叶。将及根本。揣摩排布。投抵激发。今以其已然之迹言之。一则以为理气无发挥之说。二则以为寒水衣书之可推也。三则以为泰仁语录之假托也。末乃掇拾镌党之悖说。
不以为惧。当时见此。不以为怒。则岂古人护贤之诚。不及于今人而然欤。噫嘻不难知矣。世之有一种不悦于尤遂两先生者多矣。早晚为祸。识者固已虑之。而今于状文之出。看作奇货。巧加捏诬。先攻枝叶。将及根本。揣摩排布。投抵激发。今以其已然之迹言之。一则以为理气无发挥之说。二则以为寒水衣书之可推也。三则以为泰仁语录之假托也。末乃掇拾镌党之悖说。与或人书
近日连儒事。世道之大变怪。朝野之所痛骇。馆学之重罚通头。可谓得好恶之正。尽扶抑之道。而第念连儒前后通文。不惟侵辱我师门。乃敢推上于尤庵遂庵两先生。肆然攻斥。无少忌惮。则起闹二字之罚。只知其外影之劻勷。而不识其里面之包藏也。且所谓连儒。不过受人诱䝱。元不识本事是非者。则是何足责哉。从初头主张𥳽弄者自有其人。而一世之所共知。渠辈之所自任。则只罚通头。可谓治其末而不治其本也。大抵彼辈之本心必欲诬蔑者。尤遂两先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9H 页
 也。最所怨毒者。旸谷,屏溪二长老也。何以知其然也。年前湖儒之疏出。而士论分裂。莫可收拾。旸谷,屏溪二长老移书知旧。以明遂庵先生本意。以卞尤春先后得失。则一种阴邪之徒。憾恨益深。跳踉层加。乃敢发文列邑。论罚二老。而以春门反卒,斯文乱贼为目。则其欲诬蔑二先生。其所怨毒两长老者。已自有其党矣。惟其党与甚少。机会难逢。藏形敛迹。若无为也。而欲一乘便逞憾。素蓄积也。至于沙溪后孙之不满于尤遂二先生。亦有所由。遂翁赞尤翁真像。有曰集群儒之大成。彼即以为尤翁既当大成之称。则沙溪却在群儒之列。潜怀怨怒。盖亦有年。及其旸谷状文之出。又有二先生最著之语。于是乎群憾交煽。骇机倏发。至于馆学之通而极矣。连金之自初至终。所与同事。或使之发论。或使之参会者。怀德之宋。文义之吴。前日论罚二老之徒。则其雄唱雌和。表里相应之状。有不可讳矣。彼虽以状文为把柄。而状文之本无可疵。不待此卞明而彼实知之。最初连乡通文中。以而已二字。改换状文中最著二字。改换他人文字。自是巧恶者所为。彼岂全然不知而不得不为此者。曰最著则传道诸贤。皆在著字之中矣。曰而已则传道
也。最所怨毒者。旸谷,屏溪二长老也。何以知其然也。年前湖儒之疏出。而士论分裂。莫可收拾。旸谷,屏溪二长老移书知旧。以明遂庵先生本意。以卞尤春先后得失。则一种阴邪之徒。憾恨益深。跳踉层加。乃敢发文列邑。论罚二老。而以春门反卒,斯文乱贼为目。则其欲诬蔑二先生。其所怨毒两长老者。已自有其党矣。惟其党与甚少。机会难逢。藏形敛迹。若无为也。而欲一乘便逞憾。素蓄积也。至于沙溪后孙之不满于尤遂二先生。亦有所由。遂翁赞尤翁真像。有曰集群儒之大成。彼即以为尤翁既当大成之称。则沙溪却在群儒之列。潜怀怨怒。盖亦有年。及其旸谷状文之出。又有二先生最著之语。于是乎群憾交煽。骇机倏发。至于馆学之通而极矣。连金之自初至终。所与同事。或使之发论。或使之参会者。怀德之宋。文义之吴。前日论罚二老之徒。则其雄唱雌和。表里相应之状。有不可讳矣。彼虽以状文为把柄。而状文之本无可疵。不待此卞明而彼实知之。最初连乡通文中。以而已二字。改换状文中最著二字。改换他人文字。自是巧恶者所为。彼岂全然不知而不得不为此者。曰最著则传道诸贤。皆在著字之中矣。曰而已则传道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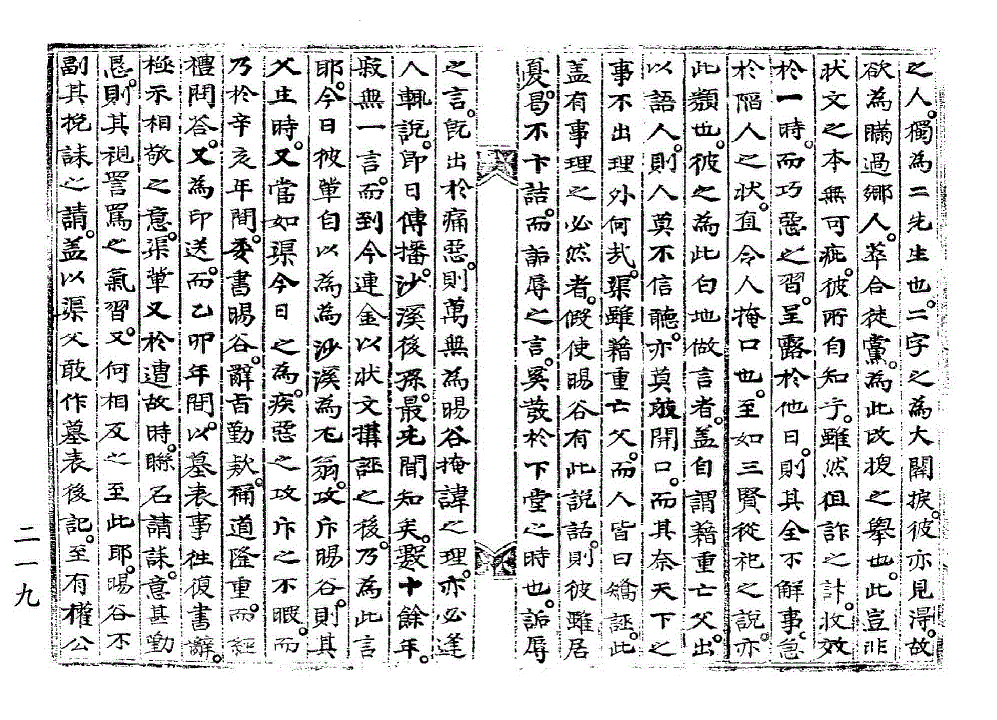 之人。独为二先生也。二字之为大关捩。彼亦见得。故欲为瞒过乡人。萃合徒党。为此改换之举也。此岂非状文之本无可疵。彼所自知乎。虽然狙诈之计。收效于一时。而巧恶之习。呈露于他日。则其全不解事。急于陷人之状。直令人掩口也。至如三贤从祀之说。亦此类也。彼之为此白地做言者。盖自谓藉重亡父。出以语人。则人莫不信听。亦莫敢开口。而其奈天下之事不出理外何哉。渠虽藉重亡父。而人皆曰矫诬。此盖有事理之必然者。假使旸谷有此说话。则彼虽居忧。曷不卞诘。而诟辱之言。奚发于下堂之时也。诟辱之言。既出于痛恶。则万无为旸谷掩讳之理。亦必逢人辄说。即日传播。沙溪后孙。最无闻知矣。数十馀年。寂无一言。而到今连金以状文搆诬之后。乃为此言耶。今日彼辈自以为为沙溪为尤翁。攻斥旸谷。则其父生时。又当如渠今日之为。疾恶之攻斥之不暇。而乃于辛亥年间。委书旸谷。辞旨勤款。称道隆重。而经礼问答。又为印送。而乙卯年间。以墓表事往复书辞。极示相敬之意。渠辈又于遭故时。联名请诔。意甚勤恳。则其视詈骂之气习。又何相反之至此耶。旸谷不副其挽诔之请。盖以渠父敢作墓表后记。至有权公
之人。独为二先生也。二字之为大关捩。彼亦见得。故欲为瞒过乡人。萃合徒党。为此改换之举也。此岂非状文之本无可疵。彼所自知乎。虽然狙诈之计。收效于一时。而巧恶之习。呈露于他日。则其全不解事。急于陷人之状。直令人掩口也。至如三贤从祀之说。亦此类也。彼之为此白地做言者。盖自谓藉重亡父。出以语人。则人莫不信听。亦莫敢开口。而其奈天下之事不出理外何哉。渠虽藉重亡父。而人皆曰矫诬。此盖有事理之必然者。假使旸谷有此说话。则彼虽居忧。曷不卞诘。而诟辱之言。奚发于下堂之时也。诟辱之言。既出于痛恶。则万无为旸谷掩讳之理。亦必逢人辄说。即日传播。沙溪后孙。最无闻知矣。数十馀年。寂无一言。而到今连金以状文搆诬之后。乃为此言耶。今日彼辈自以为为沙溪为尤翁。攻斥旸谷。则其父生时。又当如渠今日之为。疾恶之攻斥之不暇。而乃于辛亥年间。委书旸谷。辞旨勤款。称道隆重。而经礼问答。又为印送。而乙卯年间。以墓表事往复书辞。极示相敬之意。渠辈又于遭故时。联名请诔。意甚勤恳。则其视詈骂之气习。又何相反之至此耶。旸谷不副其挽诔之请。盖以渠父敢作墓表后记。至有权公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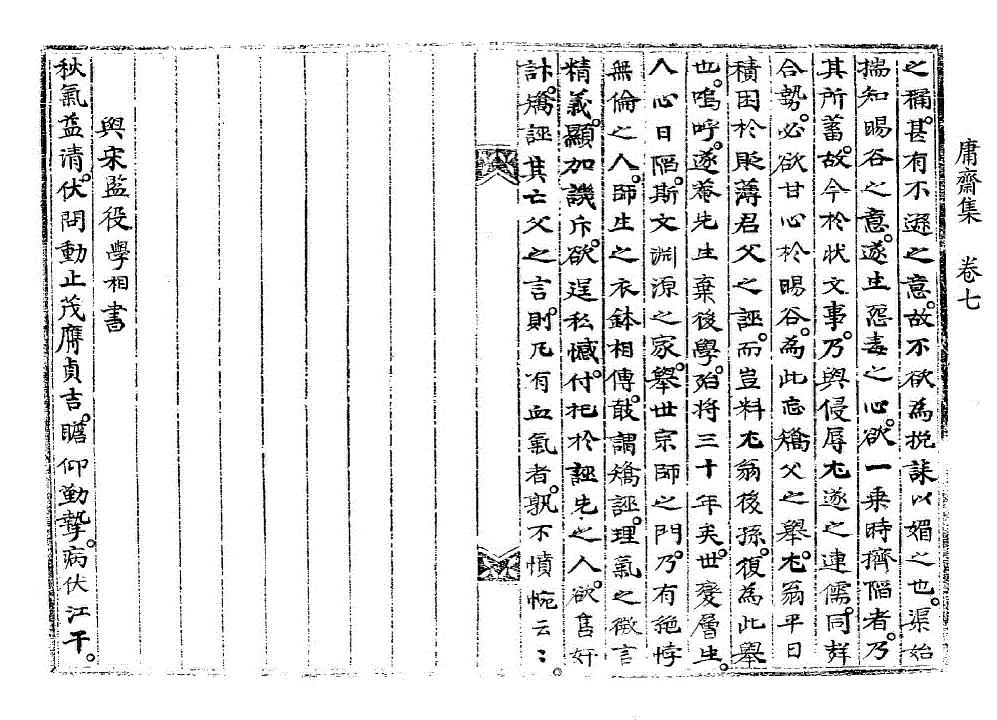 之称。甚有不逊之意。故不欲为挽诔以媚之也。渠始揣知旸谷之意。遂生怨毒之心。欲一乘时挤陷者。乃其所蓄。故今于状文事。乃与侵辱尤遂之连儒。同声合势。必欲甘心于旸谷。为此忘矫父之举。尤翁平日积困于贬薄君父之诬。而岂料尤翁后孙。复为此举也。呜呼。遂庵先生弃后学。殆将三十年矣。世变层生。人心日陷。斯文渊源之家。举世宗师之门。乃有绝悖无伦之人。师生之衣钵相传。敢谓矫诬。理气之微言精义。显加讥斥。欲逞私憾。付托于诬先之人。欲售奸计。矫诬其亡父之言。则凡有血气者。孰不愤惋云云。
之称。甚有不逊之意。故不欲为挽诔以媚之也。渠始揣知旸谷之意。遂生怨毒之心。欲一乘时挤陷者。乃其所蓄。故今于状文事。乃与侵辱尤遂之连儒。同声合势。必欲甘心于旸谷。为此忘矫父之举。尤翁平日积困于贬薄君父之诬。而岂料尤翁后孙。复为此举也。呜呼。遂庵先生弃后学。殆将三十年矣。世变层生。人心日陷。斯文渊源之家。举世宗师之门。乃有绝悖无伦之人。师生之衣钵相传。敢谓矫诬。理气之微言精义。显加讥斥。欲逞私憾。付托于诬先之人。欲售奸计。矫诬其亡父之言。则凡有血气者。孰不愤惋云云。与宋监役(学相)书
秋气益清。伏问动止茂膺贞吉。瞻仰勤挚。病伏江干。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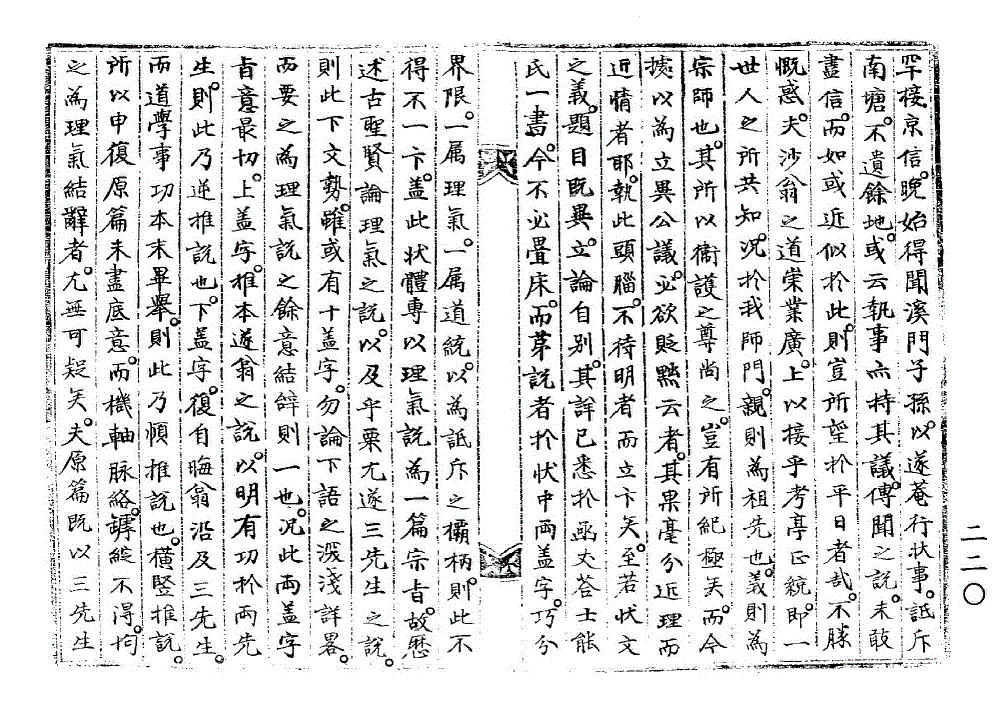 罕接京信。晚始得闻溪门子孙。以遂庵行状事。诋斥南塘。不遗馀地。或云执事亦持其议。传闻之说。未敢尽信。而如或近似于此。则岂所望于平日者哉。不胜慨惑。夫沙翁之道崇业广。上以接乎考亭正统。即一世人之所共知。况于我师门。亲则为祖先也。义则为宗师也。其所以卫护之尊尚之。岂有所纪极矣。而今据以为立异公议。必欲贬黜云者。其果毫分近理而近情者耶。执此头脑。不待明者而立卞矣。至若状文之义。题目既异。立论自别。其详已悉于函丈答士能氏一书。今不必叠床。而第说者于状中两盖字。巧分界限。一属理气。一属道统。以为诋斥之把柄。则此不得不一卞。盖此状体专以理气说为一篇宗旨。故历述古圣贤论理气之说。以及乎栗尤遂三先生之说。则此下文势。虽或有十盖字。勿论下语之深浅详略。而要之为理气说之馀意结辞则一也。况此两盖字旨意最切。上盖字。推本遂翁之说。以明有功于两先生。则此乃逆推说也。下盖字。复自晦翁沿及三先生。而道学事功本末毕举。则此乃顺推说也。横竖推说。所以申复原篇未尽底意。而机轴脉络。罅绽不得。均之为理气结辞者。尤无可疑矣。夫原篇既以三先生
罕接京信。晚始得闻溪门子孙。以遂庵行状事。诋斥南塘。不遗馀地。或云执事亦持其议。传闻之说。未敢尽信。而如或近似于此。则岂所望于平日者哉。不胜慨惑。夫沙翁之道崇业广。上以接乎考亭正统。即一世人之所共知。况于我师门。亲则为祖先也。义则为宗师也。其所以卫护之尊尚之。岂有所纪极矣。而今据以为立异公议。必欲贬黜云者。其果毫分近理而近情者耶。执此头脑。不待明者而立卞矣。至若状文之义。题目既异。立论自别。其详已悉于函丈答士能氏一书。今不必叠床。而第说者于状中两盖字。巧分界限。一属理气。一属道统。以为诋斥之把柄。则此不得不一卞。盖此状体专以理气说为一篇宗旨。故历述古圣贤论理气之说。以及乎栗尤遂三先生之说。则此下文势。虽或有十盖字。勿论下语之深浅详略。而要之为理气说之馀意结辞则一也。况此两盖字旨意最切。上盖字。推本遂翁之说。以明有功于两先生。则此乃逆推说也。下盖字。复自晦翁沿及三先生。而道学事功本末毕举。则此乃顺推说也。横竖推说。所以申复原篇未尽底意。而机轴脉络。罅绽不得。均之为理气结辞者。尤无可疑矣。夫原篇既以三先生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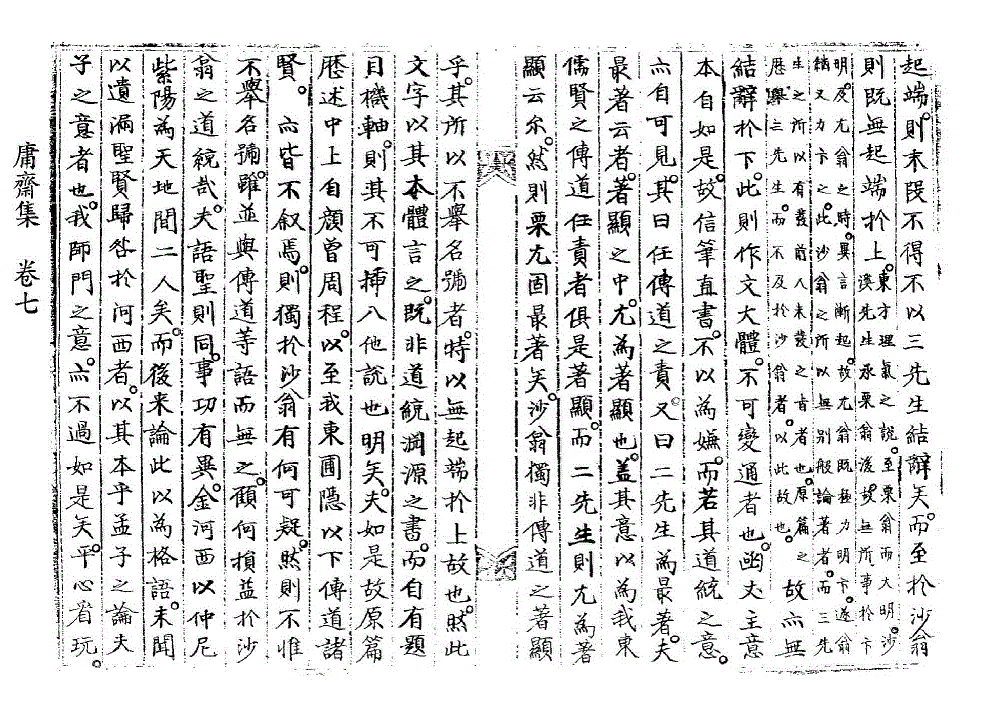 起端。则末段不得不以三先生结辞矣。而至于沙翁则既无起端于上。(东方理气之说。至栗翁而大明。沙溪先生承栗翁后。故无所事于卞明。及尤翁之时。异言渐起。故尤翁既极力明卞。遂翁继又力卞之。此沙翁之所以无别般论著者。而三先生之所以有发前人未发之旨者也。原篇之历举三先生。而不及于沙翁者。以此故也。)故亦无结辞于下。此则作文大体。不可变通者也。函丈主意本自如是。故信笔直书。不以为嫌。而若其道统之意。亦自可见。其曰任传道之责。又曰二先生为最著。夫最著云者。著显之中。尤为著显也。盖其意以为我东儒贤之传道任责者俱是著显。而二先生则尤为著显云尔。然则栗尤固最著矣。沙翁独非传道之著显乎。其所以不举名号者。特以无起端于上故也。然此文字以其本体言之。既非道统渊源之书。而自有题目机轴。则其不可插入他说也明矣。夫如是故原篇历述中上自颜曾周程。以至我东圃隐以下传道诸贤。 亦皆不叙焉。则独于沙翁有何可疑。然则不惟不举名号。虽并与传道等语而无之。顾何损益于沙翁之道统哉。夫语圣则同。事功有异。金河西以仲尼紫阳为天地间二人矣。而后来论此以为格语。未闻以遗漏圣贤归咎于河西者。以其本乎孟子之论夫子之意者也。我师门之意。亦不过如是矣。平心看玩。
起端。则末段不得不以三先生结辞矣。而至于沙翁则既无起端于上。(东方理气之说。至栗翁而大明。沙溪先生承栗翁后。故无所事于卞明。及尤翁之时。异言渐起。故尤翁既极力明卞。遂翁继又力卞之。此沙翁之所以无别般论著者。而三先生之所以有发前人未发之旨者也。原篇之历举三先生。而不及于沙翁者。以此故也。)故亦无结辞于下。此则作文大体。不可变通者也。函丈主意本自如是。故信笔直书。不以为嫌。而若其道统之意。亦自可见。其曰任传道之责。又曰二先生为最著。夫最著云者。著显之中。尤为著显也。盖其意以为我东儒贤之传道任责者俱是著显。而二先生则尤为著显云尔。然则栗尤固最著矣。沙翁独非传道之著显乎。其所以不举名号者。特以无起端于上故也。然此文字以其本体言之。既非道统渊源之书。而自有题目机轴。则其不可插入他说也明矣。夫如是故原篇历述中上自颜曾周程。以至我东圃隐以下传道诸贤。 亦皆不叙焉。则独于沙翁有何可疑。然则不惟不举名号。虽并与传道等语而无之。顾何损益于沙翁之道统哉。夫语圣则同。事功有异。金河西以仲尼紫阳为天地间二人矣。而后来论此以为格语。未闻以遗漏圣贤归咎于河西者。以其本乎孟子之论夫子之意者也。我师门之意。亦不过如是矣。平心看玩。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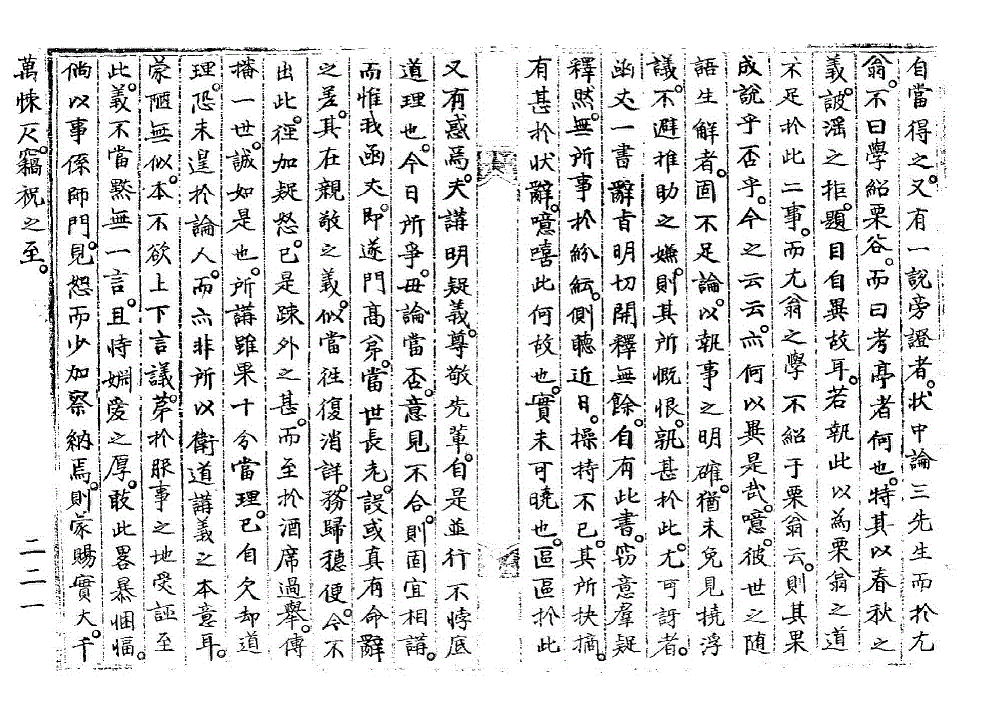 自当得之。又有一说旁證者。状中论三先生而于尤翁。不曰学绍栗谷。而曰考亭者何也。特其以春秋之义。诐淫之拒。题目自异故耳。若执此以为栗翁之道不足于此二事。而尤翁之学不绍于栗翁云。则其果成说乎否乎。今之云云。亦何以异是哉。噫。彼世之随语生解者。固不足论。以执事之明确。犹未免见挠浮议。不避推助之嫌。则其所慨恨。孰甚于此。尤可讶者。函丈一书辞旨明切开释无馀。自有此书。窃意群疑释然。无所事于纷纭。侧听近日。操持不已。其所抉摘。有甚于状辞。噫嘻此何故也。实未可晓也。区区于此又有惑焉。夫讲明疑义。尊敬先辈。自是并行不悖底道理也。今日所争。毋论当否。意见不合。则固宜相讲。而惟我函丈。即遂门高弟。当世长老。设或真有命辞之差。其在亲敬之义。似当往复消详。务归稳便。今不出此。径加疑怒。已是疏外之甚。而至于酒席过举。传播一世。诚如是也。所讲虽果十分当理。已自欠却道理。恐未遑于论人。而亦非所以卫道讲义之本意耳。蒙陋无似。本不欲上下言议。第于服事之地受诬至此。义不当默无一言。且恃姻爱之厚。敢此略暴悃愊。倘以事系师门。见恕而少加察纳焉。则蒙赐实大。千万悚仄。窃祝之至。
自当得之。又有一说旁證者。状中论三先生而于尤翁。不曰学绍栗谷。而曰考亭者何也。特其以春秋之义。诐淫之拒。题目自异故耳。若执此以为栗翁之道不足于此二事。而尤翁之学不绍于栗翁云。则其果成说乎否乎。今之云云。亦何以异是哉。噫。彼世之随语生解者。固不足论。以执事之明确。犹未免见挠浮议。不避推助之嫌。则其所慨恨。孰甚于此。尤可讶者。函丈一书辞旨明切开释无馀。自有此书。窃意群疑释然。无所事于纷纭。侧听近日。操持不已。其所抉摘。有甚于状辞。噫嘻此何故也。实未可晓也。区区于此又有惑焉。夫讲明疑义。尊敬先辈。自是并行不悖底道理也。今日所争。毋论当否。意见不合。则固宜相讲。而惟我函丈。即遂门高弟。当世长老。设或真有命辞之差。其在亲敬之义。似当往复消详。务归稳便。今不出此。径加疑怒。已是疏外之甚。而至于酒席过举。传播一世。诚如是也。所讲虽果十分当理。已自欠却道理。恐未遑于论人。而亦非所以卫道讲义之本意耳。蒙陋无似。本不欲上下言议。第于服事之地受诬至此。义不当默无一言。且恃姻爱之厚。敢此略暴悃愊。倘以事系师门。见恕而少加察纳焉。则蒙赐实大。千万悚仄。窃祝之至。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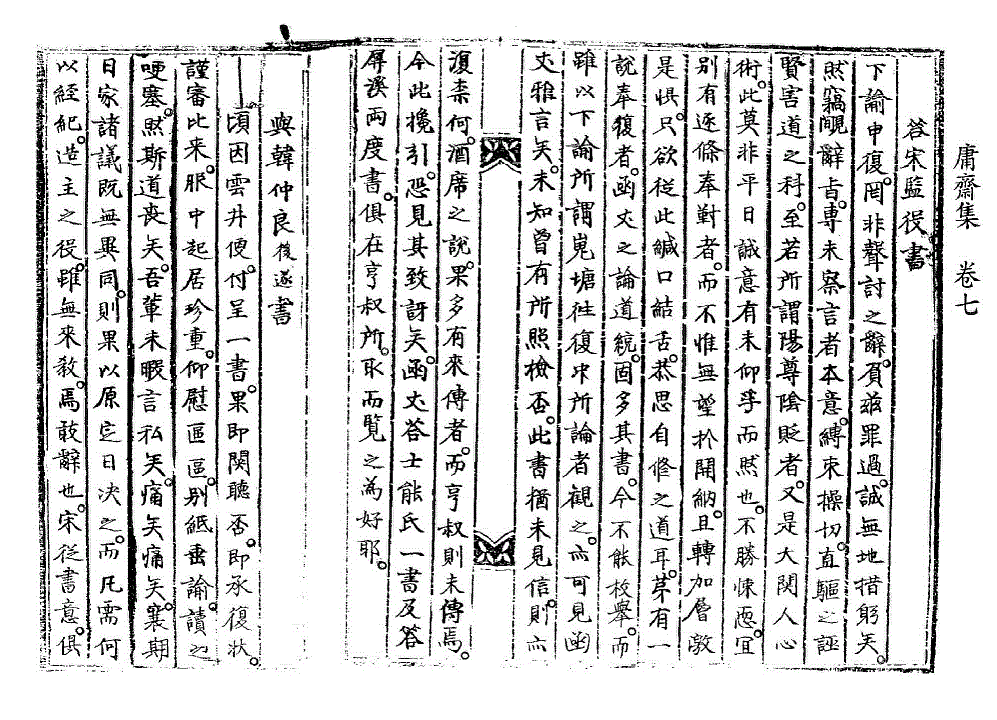 答宋监役书
答宋监役书下谕申复。罔非声讨之辞。负玆罪过。诚无地措躬矣。然窃覸辞旨。专未察言者本意。缚束操切。直驱之诬贤害道之科。至若所谓阳尊阴贬者。又是大关人心术。此莫非平日诚意有未仰孚而然也。不胜悚恧。宜别有逐条奉对者。而不惟无望于开纳。且转加层激是惧。只欲从此缄口结舌。恭思自修之道耳。第有一说奉复者。函丈之论道统。固多其书。今不能枚举。而虽以下谕所谓嵬塘往复中所论者观之。亦可见函丈雅言矣。未知曾有所照检否。此书犹未见信。则亦复柰何。酒席之说。果多有来传者。而亨叔则未传焉。今此搀引。恐见其致讶矣。函丈答士能氏一书及答屏溪两度书。俱在亨叔所。取而览之为好耶。
与韩仲良(后遂)书
顷因云井便。付呈一书。果即关听否。即承复状。谨审比来。服中起居珍重。仰慰区区。别纸垂谕。读之哽塞。然斯道丧矣。吾辈未暇言私矣。痛矣痛矣。襄期日家诸议既无异同。则果以原定日决之。而凡需何以经纪。造主之役。虽无来教。焉敢辞也。宋从书意。俱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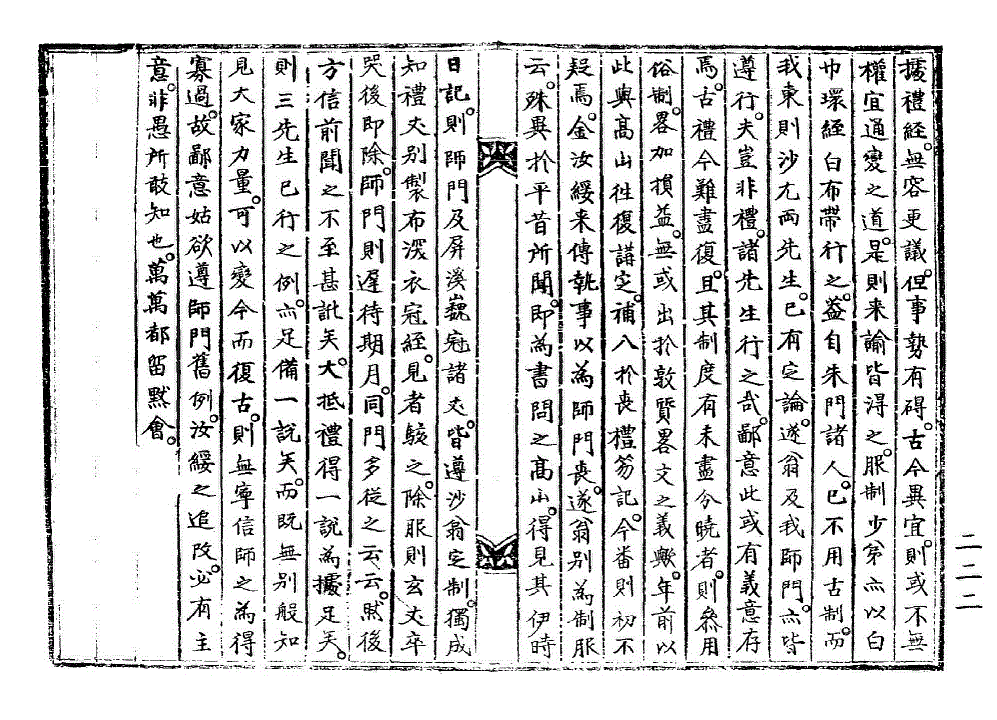 据礼经。无容更议。但事势有碍。古今异宜。则或不无权宜通变之道。是则来谕皆得之。服制少弟亦以白巾环绖白布带行之。盖自朱门诸人。已不用古制。而我东则沙尤两先生。已有定论。遂翁及我师门。亦皆遵行。夫岂非礼。诸先生行之哉。鄙意此或有义意存焉。古礼今难尽复。且其制度有未尽分晓者。则参用俗制。略加损益。无或出于敦质略文之义欤。年前以此与高山往复讲定。补入于丧礼笏记。今番则初不疑焉。金汝绥来传执事以为师门丧。遂翁别为制服云。殊异于平昔所闻。即为书问之高山。得见其伊时日记。则师门及屏溪巍冠诸丈。皆遵沙翁定制。独成知礼丈别制布深衣冠绖。见者骇之。除服则玄丈卒哭后即除。师门则迟待期月。同门多从之云云。然后方信前闻之不至甚讹矣。大抵礼得一说为据足矣。则三先生已行之例。亦足备一说矣。而既无别般知见大家力量。可以变今而复古。则无宁信师之为得寡过。故鄙意姑欲遵师门旧例。汝绥之追改。必有主意。非愚所敢知也。万万都留默会。
据礼经。无容更议。但事势有碍。古今异宜。则或不无权宜通变之道。是则来谕皆得之。服制少弟亦以白巾环绖白布带行之。盖自朱门诸人。已不用古制。而我东则沙尤两先生。已有定论。遂翁及我师门。亦皆遵行。夫岂非礼。诸先生行之哉。鄙意此或有义意存焉。古礼今难尽复。且其制度有未尽分晓者。则参用俗制。略加损益。无或出于敦质略文之义欤。年前以此与高山往复讲定。补入于丧礼笏记。今番则初不疑焉。金汝绥来传执事以为师门丧。遂翁别为制服云。殊异于平昔所闻。即为书问之高山。得见其伊时日记。则师门及屏溪巍冠诸丈。皆遵沙翁定制。独成知礼丈别制布深衣冠绖。见者骇之。除服则玄丈卒哭后即除。师门则迟待期月。同门多从之云云。然后方信前闻之不至甚讹矣。大抵礼得一说为据足矣。则三先生已行之例。亦足备一说矣。而既无别般知见大家力量。可以变今而复古。则无宁信师之为得寡过。故鄙意姑欲遵师门旧例。汝绥之追改。必有主意。非愚所敢知也。万万都留默会。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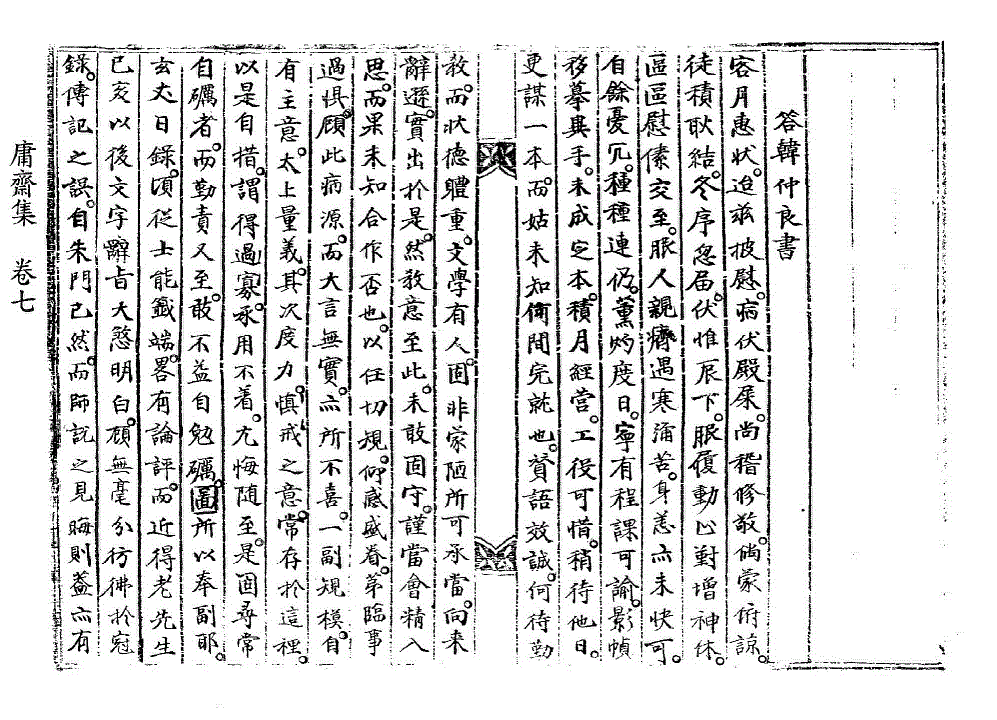 答韩仲良书
答韩仲良书客月惠状。迨玆披慰。病伏殿屎。尚稽修敬。倘蒙俯谅。徒积耿结。冬序忽届。伏惟辰下。服履动止对增神休。区区慰傃交至。服人亲癠遇寒弥苦。身恙亦未快可。自馀忧冗。种种连仍。薰灼度日。宁有程课可谕。影帧移摹异手。未成定本。积月经营。工役可惜。稍待他日。更谋一本。而姑未知何间完就也。赞语效诚。何待勤教。而状德体重。文学有人。固非蒙陋所可承当。向来辞逊。实出于是。然教意至此。未敢固守。谨当会精入思。而果未知合作否也。以任切规。仰感盛眷。第临事过惧。顾此病源。而大言无实。亦所不喜。一副规模。自有主意。太上量义。其次度力。戒慎之意。常存于这里。以是自措。谓得寡过。承用不着。尤悔随至。是固寻常自砺者。而勤责又至。敢不益自勉砺。图所以奉副耶。玄丈日录。顷从士能签端。略有论评。而近得老先生己亥以后文字辞旨大煞明白。顾无毫分彷佛于冠录。传记之误。自朱门已然。而师说之见晦则盖亦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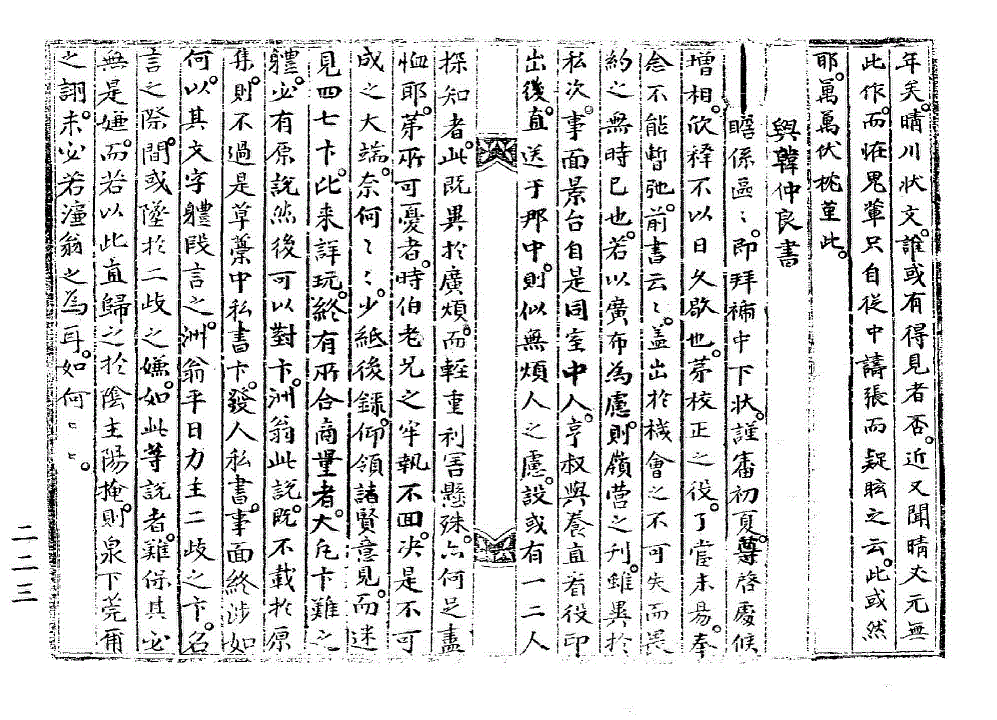 年矣。晴川状文。谁或有得见者否。近又闻晴丈元无此作。而怪鬼辈只自从中诪张而疑眩之云。此或然耶。万万伏枕堇此。
年矣。晴川状文。谁或有得见者否。近又闻晴丈元无此作。而怪鬼辈只自从中诪张而疑眩之云。此或然耶。万万伏枕堇此。与韩仲良书
瞻系区区。即拜褫中下状。谨审初夏。尊启处候增相。欣释不以日久歇也。第校正之役。了当未易。奉念不能暂弛。前书云云。盖出于机会之不可失而畏约之无时已也。若以广布为虑。则岭营之刊。虽异于私次。事面景台自是同室中人。亨叔与养直看役印出。直送于那中。则似无烦人之虑。设或有一二人探知者。此既异于广烦。而轻重利害悬殊。亦何足尽恤耶。第所可忧者。时伯老兄之牢执不回。决是不可成之大端。奈何奈何。少纸后录。仰领诸贤意见。而迷见四七卞。比来详玩。终有所合商量者。大凡卞难之体。必有原说然后可以对卞。洲翁此说。既不载于原集。则不过是草藁中私书卞。发人私书。事面终涉如何。以其文字体段言之。洲翁平日力主二歧之卞。名言之际。间或坠于二歧之嫌。如此等说者。难保其必无是嫌。而若以此直归之于阴主阳掩。则泉下莞尔之诩。未必若濂翁之为耳。如何如何。
与韩仲良书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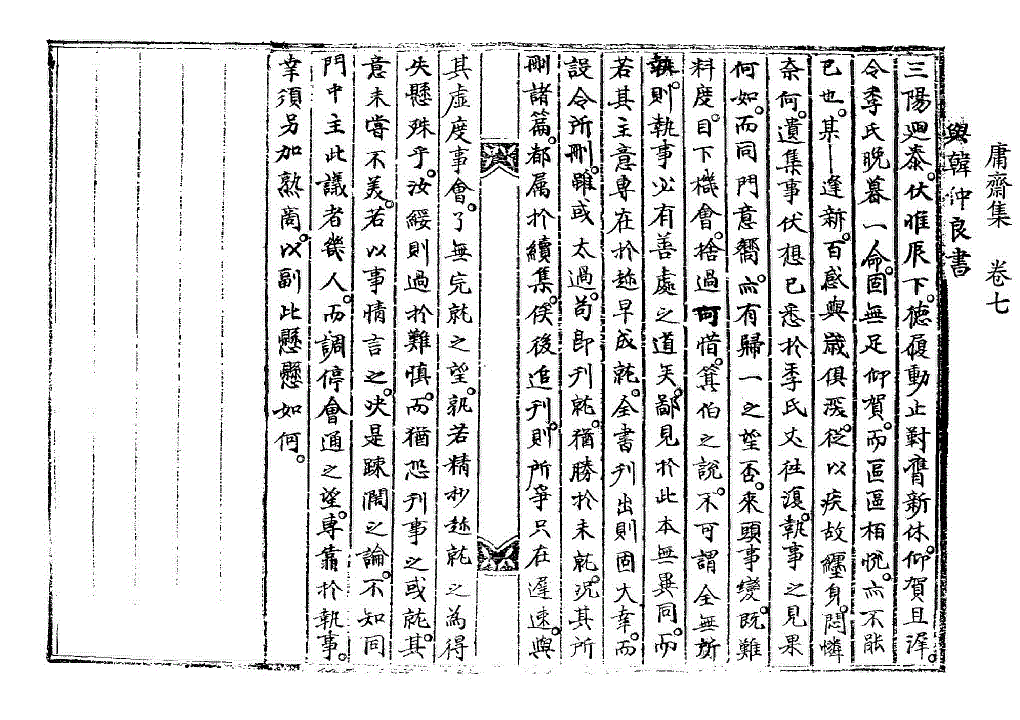 三阳回泰。伏惟辰下。德履动止对膺新休。仰贺且溯。令季氏晚暮一命。固无足仰贺。而区区柏悦。亦不能已也。某逢新。百感与岁俱深。从以疾故缠身。闷怜奈何。遗集事伏想已悉于季氏丈往复。执事之见果何如。而同门意向。亦有归一之望否。来头事变。既难料度。目下机会。舍过可惜。箕伯之说。不可谓全无所执。则执事必有善处之道矣。鄙见于此本无异同。而若其主意专在于趁早成就。全书刊出则固大幸。而设令所删。虽或太过。苟即刊就。犹胜于未就。况其所删诸篇。都属于续集。俟后追刊。则所争只在迟速。与其虚度事会。了无完就之望。孰若精抄趁就之为得失悬殊乎。汝绥则过于难慎。而犹恐刊事之或就。其意未尝不美。若以事情言之。决是疏阔之论。不知同门中主此议者几人。而调停会通之望。专靠于执事。幸须另加熟商。以副此悬悬如何。
三阳回泰。伏惟辰下。德履动止对膺新休。仰贺且溯。令季氏晚暮一命。固无足仰贺。而区区柏悦。亦不能已也。某逢新。百感与岁俱深。从以疾故缠身。闷怜奈何。遗集事伏想已悉于季氏丈往复。执事之见果何如。而同门意向。亦有归一之望否。来头事变。既难料度。目下机会。舍过可惜。箕伯之说。不可谓全无所执。则执事必有善处之道矣。鄙见于此本无异同。而若其主意专在于趁早成就。全书刊出则固大幸。而设令所删。虽或太过。苟即刊就。犹胜于未就。况其所删诸篇。都属于续集。俟后追刊。则所争只在迟速。与其虚度事会。了无完就之望。孰若精抄趁就之为得失悬殊乎。汝绥则过于难慎。而犹恐刊事之或就。其意未尝不美。若以事情言之。决是疏阔之论。不知同门中主此议者几人。而调停会通之望。专靠于执事。幸须另加熟商。以副此悬悬如何。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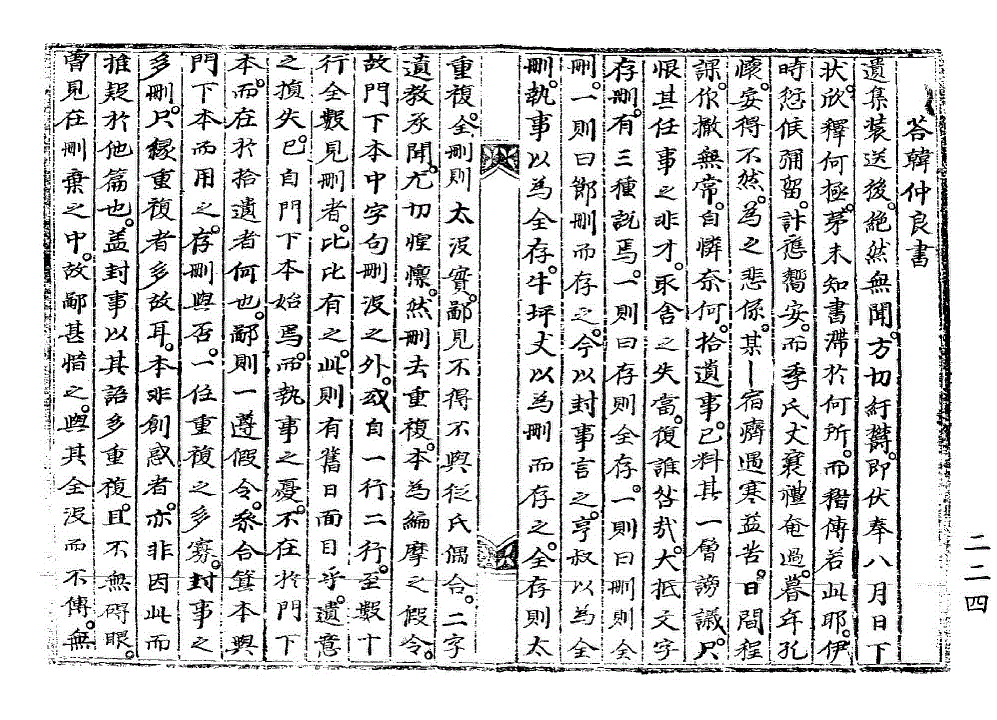 答韩仲良书
答韩仲良书遗集装送后。绝然无闻。方切纡郁。即伏奉八月日下状。欣释何极。第未知书滞于何所。而稽传若此耶。伊时愆候弥留。计应向安。而季氏丈襄礼奄过。暮年孔怀。安得不然。为之悲系。某宿癠遇寒益苦。日间程课。作撤无常。自怜奈何。拾遗事。已料其一层谤议。只恨其任事之非才。取舍之失当。复谁咎哉。大抵文字存删。有三种说焉。一则曰存则全存。一则曰删则全删。一则曰节删而存之。今以封事言之。亨叔以为全删。执事以为全存。牛坪丈以为删而存之。全存则太重复。全删则太没实。鄙见不得不与从氏偶合。二字遗教承闻。尤切惶懔。然删去重复。本为编摩之假令。故门下本中字句删没之外。或自一行二行。至数十行全数见删者。比比有之。此则有旧日面目乎。遗意之损失。已自门下本始焉。而执事之忧。不在于门下本。而在于拾遗者何也。鄙则一遵假令。参合箕本与门下本而用之。存删与否。一任重复之多寡。封事之多删。只缘重复者多故耳。本非创惑者。亦非因此而推疑于他篇也。盖封事以其语多重复。且不无碍眼。曾见在删弃之中。故鄙甚惜之。与其全没而不传。无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5H 页
 宁节删之为愈。毕竟与从氏议合。特置拾遗之首者。苦心所在也。今反以节删为罪。诚非始虑之攸出。然无论原集与拾遗。本非全书完本。要之十分精约。以备目下翻阅。日后全本出时。并与其重复者而合为成书。则可得两占便宜。区区所料量者在此。曾已累陈迷滞。或蒙记有否。深藏勿布。本来所愿。今于来示。敢不欣奉。
宁节删之为愈。毕竟与从氏议合。特置拾遗之首者。苦心所在也。今反以节删为罪。诚非始虑之攸出。然无论原集与拾遗。本非全书完本。要之十分精约。以备目下翻阅。日后全本出时。并与其重复者而合为成书。则可得两占便宜。区区所料量者在此。曾已累陈迷滞。或蒙记有否。深藏勿布。本来所愿。今于来示。敢不欣奉。答韩圣能(后述)书
东津失掺。耿与病深。崇牍远至。洽慰馀怀。矧谛冱阴。返税膺休。奉安真帧。感慕当新。肉色差爽。来示诚然。为今之计。更待旧工。而传神之法。不在笔舌。毕竟完就。亦未可必。归寻旧业。所讲何书。阳春白雪。自有其时。勤则有成。愿勿自沮。科斗时尚。固非雅习。因噎废食。古人攸讥。重理宿研。略加修润。如何如何。朝议方张。徽仪将举。龙湫雷动。亦在早晚。东岗之睡。恐不得牢矣。岁暮伏枕。瞻想益苦。湖月连床。徒入梦境。只冀增休。远副区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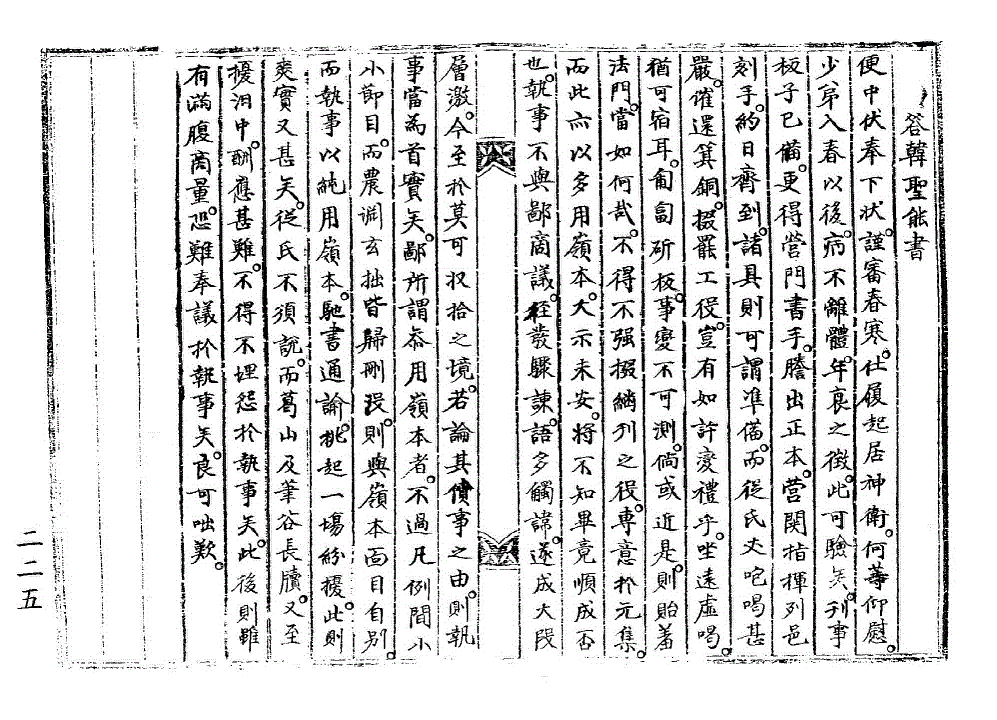 答韩圣能书
答韩圣能书便中伏奉下状。谨审春寒。仕履起居神卫。何等仰慰。少弟入春以后。病不离体。年衰之徵。此可验矣。刊事板子已备。更得营门书手。誊出正本。营关指挥列邑刻手。约日齐到。诸具则可谓准备。而从氏丈咆喝甚严。催还箕铜。掇罢工役。岂有如许变礼乎。坐远虚喝。犹可宿耳。匍匐斫板。事变不可测。倘或近是。则贻羞法门。当如何哉。不得不强掇继刊之役。专意于元集。而此亦以多用岭本。大示未安。将不知毕竟顺成否也。执事不与鄙商议。径发骤谏。语多触讳。遂成大段层激。今至于莫可收拾之境。若论其偾事之由。则执事当为首实矣。鄙所谓参用岭本者。不过凡例间小小节目。而农渊玄拙皆归删没。则与岭本面目自别。而执事以纯用岭本。驰书通谕。挑起一场纷扰。此则爽实又甚矣。从氏不须说。而葛山及笔谷长牍。又至扰汩中。酬应甚难。不得不埋怨于执事矣。此后则虽有满腹商量。恐难奉议于执事矣。良可咄叹。
答韩时伯(后殷)别纸
斯学之斯。小学之谓云云。
此学字本指大学而言。下一大字。义可见矣。大抵此篇本兼大小言之。故洒扫应对。斯学之小者也。穷理修身。斯学之大者也。对待说出。界限分明。若以在题辞之中而皆以为小学之工。则所谓德崇业广者。亦可谓之小学之事乎。道德崇深。事业广博。尧舜孔孟。方可当之。则其可责之于八岁之学乎。德崇业广。既不得为小学之事。则穷理修身。亦不可异同看矣。
蹈袭前言云云。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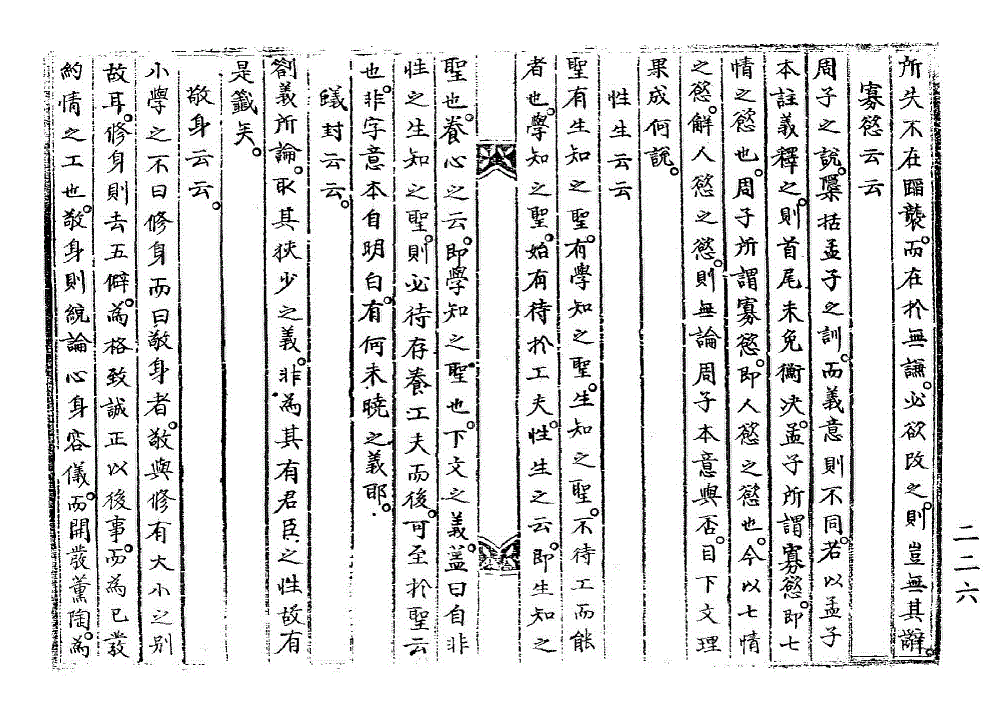 所失不在蹈袭。而在于无谦。必欲改之。则岂无其辞。
所失不在蹈袭。而在于无谦。必欲改之。则岂无其辞。寡欲云云。
周子之说。檃括孟子之训。而义意则不同。若以孟子本注义释之。则首尾未免衡决。孟子所谓寡欲。即七情之欲也。周子所谓寡欲。即人欲之欲也。今以七情之欲。解人欲之欲。则无论周子本意与否。目下文理果成何说。
性生云云。
圣有生知之圣。有学知之圣。生知之圣。不待工而能者也。学知之圣。始有待于工夫。性生之云。即生知之圣也。养心之云。即学知之圣也。下文之义。盖曰自非性之生知之圣。则必待存养工夫而后。可至于圣云也。非字意本自明白。有何未晓之义耶。
蚁封云云。
劄义所论。取其狭少之义。非为其有君臣之性故有是签矣。
敬身云云。
小学之不曰修身而曰敬身者。敬与修有大小之别故耳。修身则去五僻。为格致诚正以后事。而为已发约情之工也。敬身则统论心身容仪。而开发薰陶。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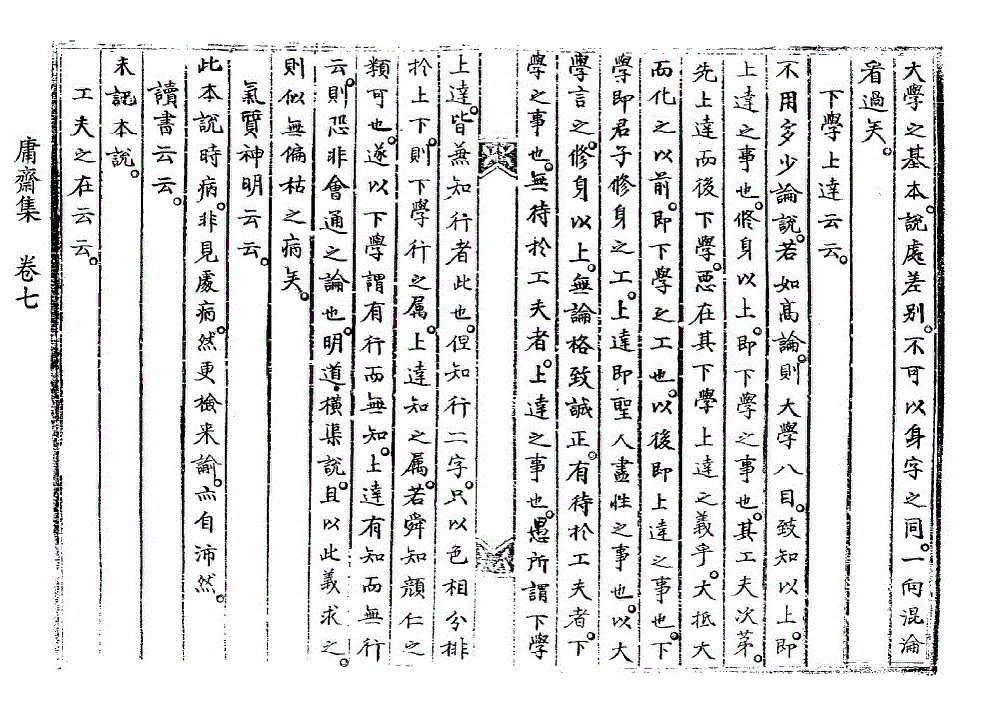 大学之基本。说处差别。不可以身字之同。一向混沦看过矣。
大学之基本。说处差别。不可以身字之同。一向混沦看过矣。下学上达云云。
不用多少论说。若如高论。则大学八目。致知以上。即上达之事也。修身以上。即下学之事也。其工夫次第。先上达而后下学。恶在其下学上达之义乎。大抵大而化之以前。即下学之工也。以后即上达之事也。下学即君子修身之工。上达即圣人尽性之事也。以大学言之。修身以上。无论格致诚正。有待于工夫者。下学之事也。无待于工夫者。上达之事也。愚所谓下学上达。皆兼知行者此也。但知行二字。只以色相分排于上下。则下学行之属。上达知之属。若舜知颜仁之类可也。遂以下学谓有行而无知。上达有知而无行云。则恐非会通之论也。明道,横渠说。且以此义求之。则似无偏枯之病矣。
气质神明云云。
此本说时病。非见处病。然更检来谕。亦自沛然。
读书云云。
未记本说。
工夫之在云云。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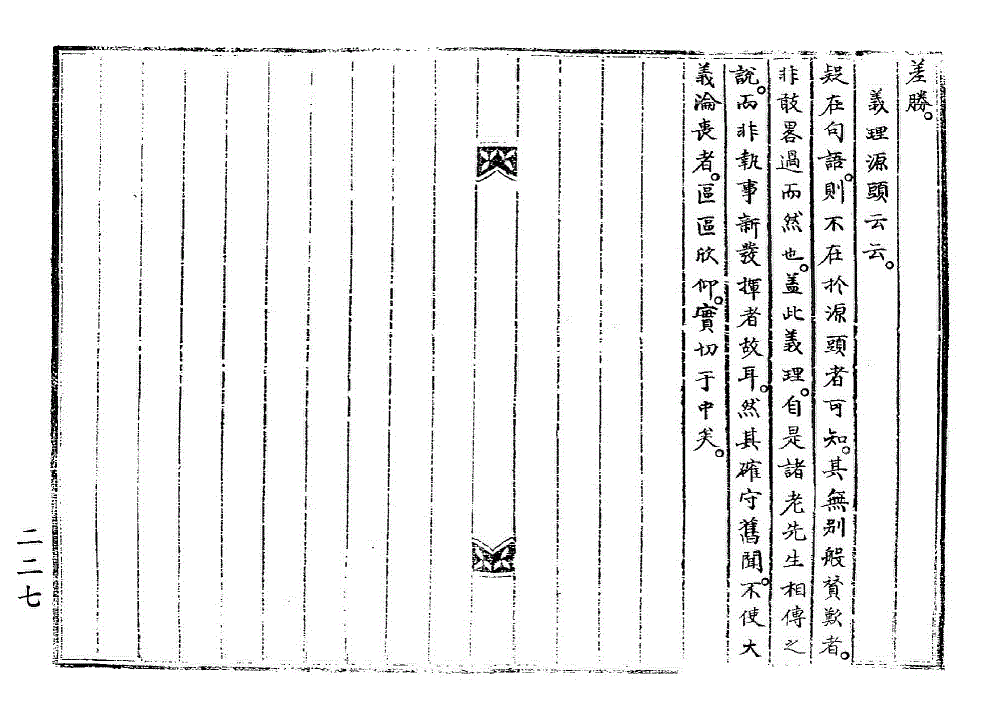 差胜。
差胜。义理源头云云。
疑在句语。则不在于源头者可知。其无别般赞叹者。非敢略过而然也。盖此义理。自是诸老先生相传之说。而非执事新发挥者故耳。然其确守旧闻。不使大义沦丧者。区区欣仰。实切于中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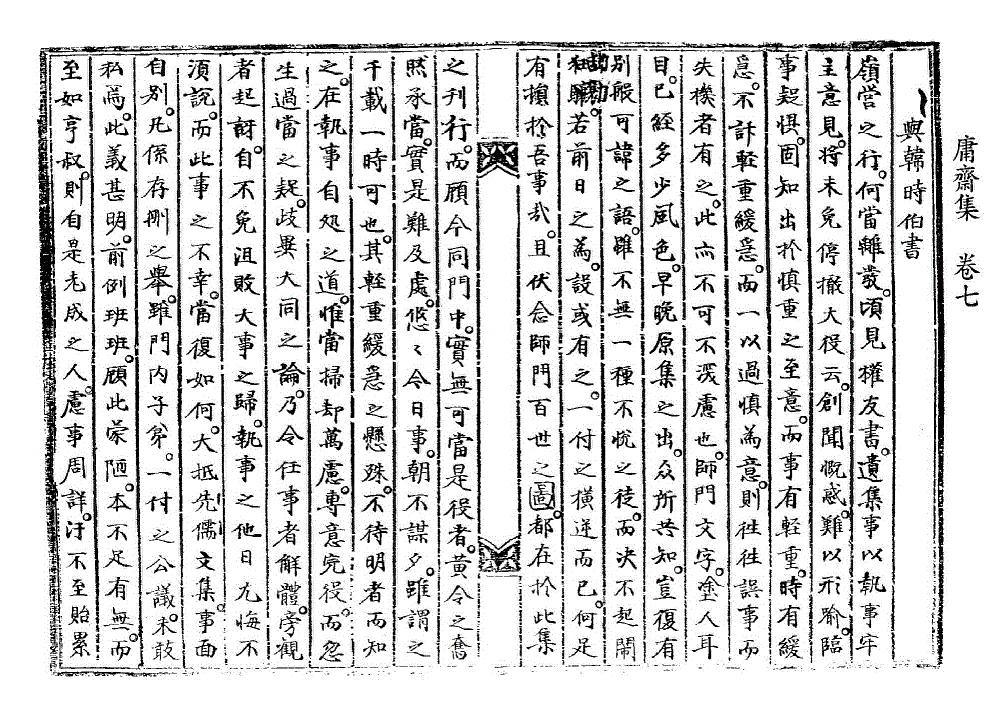 与韩时伯书
与韩时伯书岭营之行。何当离发。顷见权友书。遗集事以执事牢主意见。将未免停撤大役云。创闻慨惑。难以形喻。临事疑惧。固知出于慎重之至意。而事有轻重。时有缓急。不计轻重缓急。而一以过慎为意。则往往误事而失机者有之。此亦不可不深虑也。师门文字。涂人耳目。已经多少风色。早晚原集之出。众所共知。岂复有别般可讳之语。虽不无一种不悦之徒。而决不起闹劻勷。若前日之为。设或有之。一付之横逆而已。何足有损于吾事哉。且伏念师门百世之图。都在于此集之刊行。而顾今同门中。实无可当是役者。黄令之奋然承当。实是难及处。悠悠今日事。朝不谋夕。虽谓之千载一时可也。其轻重缓急之悬殊。不待明者而知之。在执事自处之道。惟当扫却万虑。专意完役。而忽生过当之疑。歧异大同之论。乃令任事者解体。旁观者起讶。自不免沮败大事之归。执事之他日尤悔不须说。而此事之不幸。当复如何。大抵儒先文集。事面自别。凡系存删之举。虽门内子弟。一付之公议。未敢私焉。此义甚明。前例班班。顾此蒙陋。本不足有无。而至如亨叔。则自是老成之人。虑事周详。污不至贻累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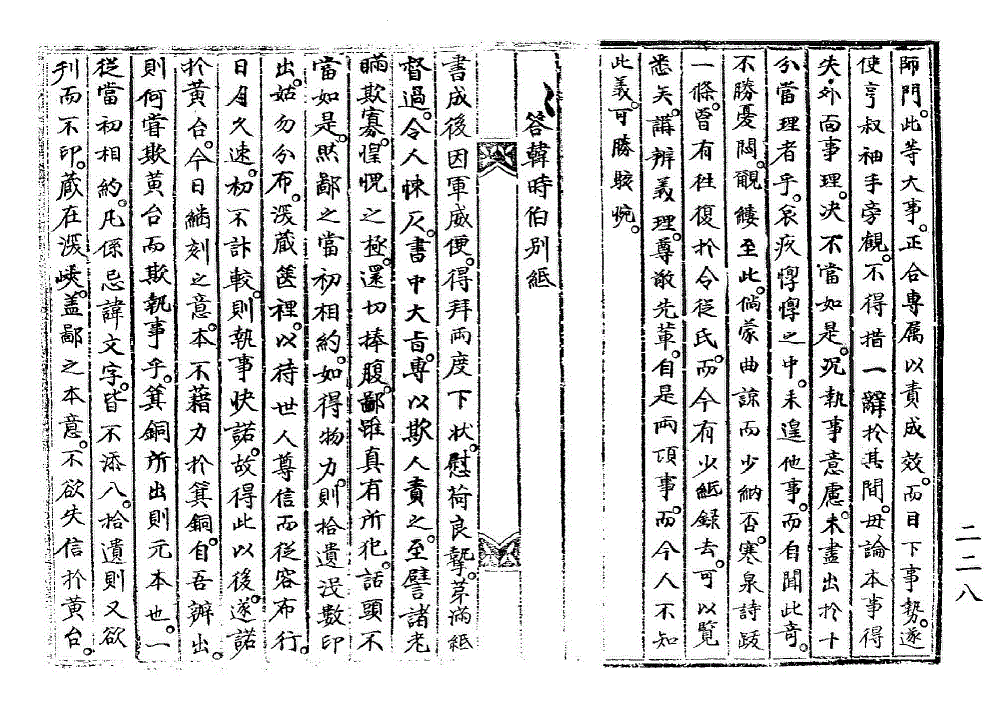 师门。此等大事。正合专属以责成效。而目下事势。遂使亨叔袖手旁观。不得措一辞于其间。毋论本事得失外面事理。决不当如是。况执事意虑。未尽出于十分当理者乎。哀疚茕茕之中。未遑他事。而自闻此奇。不胜忧闷。覼缕至此。倘蒙曲谅而少纳否。寒泉诗跋一条。曾有往复于令从氏。而今有少纸录去。可以览悉矣。讲辨义理。尊敬先辈。自是两项事。而今人不知此义。可胜骇惋。
师门。此等大事。正合专属以责成效。而目下事势。遂使亨叔袖手旁观。不得措一辞于其间。毋论本事得失外面事理。决不当如是。况执事意虑。未尽出于十分当理者乎。哀疚茕茕之中。未遑他事。而自闻此奇。不胜忧闷。覼缕至此。倘蒙曲谅而少纳否。寒泉诗跋一条。曾有往复于令从氏。而今有少纸录去。可以览悉矣。讲辨义理。尊敬先辈。自是两项事。而今人不知此义。可胜骇惋。答韩时伯别纸
书成后因军威便。得拜两度下状。慰荷良挚。第满纸督过。令人悚仄。书中大旨。专以欺人责之。至譬诸老瞒欺寡。惶愧之极。还切捧腹。鄙虽真有所犯。话头不当如是。然鄙之当初相约。如得物力。则拾遗没数印出。姑勿分布。深藏箧里。以待世人尊信而从容布行。日月久速。初不计较。则执事快诺。故得此以后。遂诺于黄台。今日继刻之意。本不藉力于箕铜。自吾办出。则何尝欺黄台而欺执事乎。箕铜所出则元本也。一从当初相约。凡系忌讳文字。皆不添入。拾遗则又欲刊而不印。藏在深峡。盖鄙之本意。不欲失信于黄台。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9H 页
 必欲践言于执事。▣▣▣▣▣▣▣▣▣▣▣▣▣▣引喻恐未得当。果无物力。则延至十年廿年。未为不可。而如有一分变通之道。失此机会。遂至于蹉跎湮没。则不敏之得罪师门。当复如何。执事本意。鄙实不知。所谓追刊拾遗之说。本欲防人急刊之意。而自家之意。仍欲删没。使不得出世耶。抑或发悸于触讳生梗。而迟待他日。若前说之云耶。由前之说。则无复可论。而由后之说。则吾辈一队老死之后。谁复捡拾此书。吾虽老而不死。如未得官力。则抚书悼叹而已。当此之时。设或是非稍定。议论归一。而其无物力难办何。苦心所在。只欲献忠于先师。执事之迂滞不思之见。有不敢恤矣。执事终不觉悟。生梗于传后大事则此亦命也。亦复奈何。只自停役以待他日议定。执事以为如何。元本目录书送。详览则可悉鄙意矣。岭本参用。不过添入示同志等诸条。而此是大篇文字。箕本以其卷秩稍多。一并见删。岂不可惜乎。其他添入。各自有说。详录于目录之下。而至于巍书见删。以其文字浩汗。且考巍集。无一字紧关见落者。则执事初云者。皆是过虑。虽以巍书言之。语不择发。讥讪备至。本集所载者。已极不满。而重复载录。以骇人眼。尤
必欲践言于执事。▣▣▣▣▣▣▣▣▣▣▣▣▣▣引喻恐未得当。果无物力。则延至十年廿年。未为不可。而如有一分变通之道。失此机会。遂至于蹉跎湮没。则不敏之得罪师门。当复如何。执事本意。鄙实不知。所谓追刊拾遗之说。本欲防人急刊之意。而自家之意。仍欲删没。使不得出世耶。抑或发悸于触讳生梗。而迟待他日。若前说之云耶。由前之说。则无复可论。而由后之说。则吾辈一队老死之后。谁复捡拾此书。吾虽老而不死。如未得官力。则抚书悼叹而已。当此之时。设或是非稍定。议论归一。而其无物力难办何。苦心所在。只欲献忠于先师。执事之迂滞不思之见。有不敢恤矣。执事终不觉悟。生梗于传后大事则此亦命也。亦复奈何。只自停役以待他日议定。执事以为如何。元本目录书送。详览则可悉鄙意矣。岭本参用。不过添入示同志等诸条。而此是大篇文字。箕本以其卷秩稍多。一并见删。岂不可惜乎。其他添入。各自有说。详录于目录之下。而至于巍书见删。以其文字浩汗。且考巍集。无一字紧关见落者。则执事初云者。皆是过虑。虽以巍书言之。语不择发。讥讪备至。本集所载者。已极不满。而重复载录。以骇人眼。尤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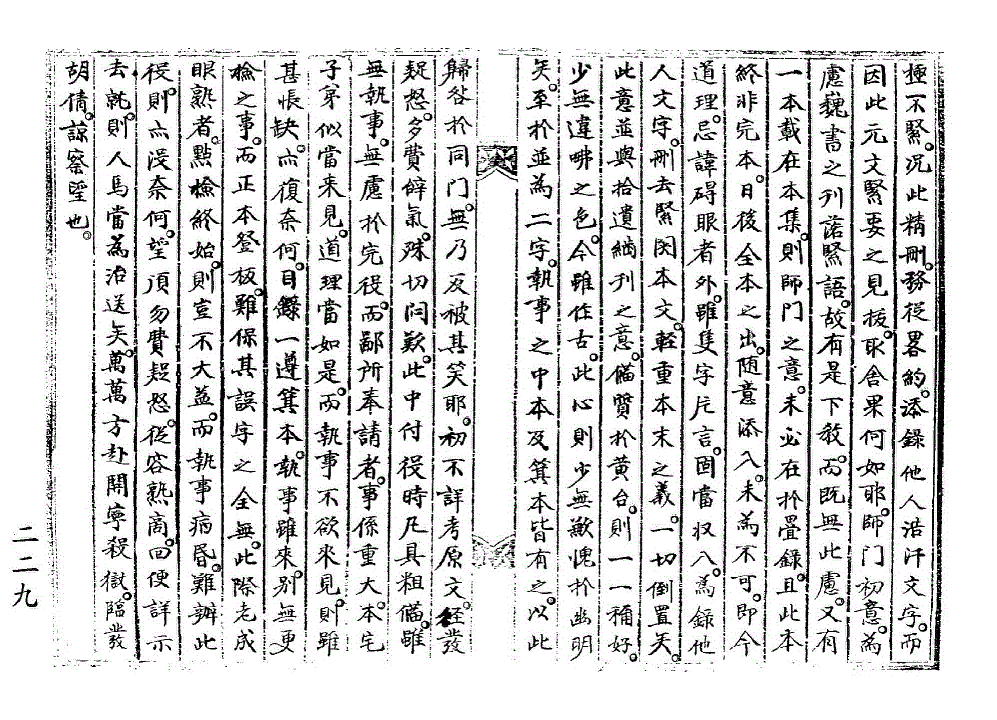 极不紧。况此精删。务从略约。添录他人浩汗文字。而因此元文紧要之见拔。取舍果何如耶。师门初意。为虑巍书之刊落紧语。故有是下教。而既无此虑。又有一本载在本集。则师门之意。未必在于叠录。且此本终非完本。日后全本之出。随意添入。未为不可。即今道理。忌讳碍眼者外。虽只字片言。固当收入。为录他人文字。删去紧关本文。轻重本末之义。一切倒置矣。此意并与拾遗继刊之意。备质于黄台。则一一称好。少无违咈之色。今虽作古。此心则少无歉愧于幽明矣。至于并为二字。执事之中本及箕本皆有之。以此归咎于同门。无乃反被其笑耶。初不详考原文。径发疑怒。多费辞气。殊切闷叹。此中付役时凡具粗备。虽无执事。无虑于完役。而鄙所奉请者。事系重大。本宅子弟似当来见。道理当如是。而执事不欲来见。则虽甚怅缺。亦复奈何。目录一遵箕本。执事虽来。别无更捡之事。而正本登板。难保其误字之全无。此际老成眼熟者。点捡终始。则岂不大益。而执事病昏。难办此役。则亦没奈何。望须勿费疑怒。从容熟商。回便详示去就。则人马当为治送矣。万万方赴开宁杀狱。临发胡倩。谅察望也。
极不紧。况此精删。务从略约。添录他人浩汗文字。而因此元文紧要之见拔。取舍果何如耶。师门初意。为虑巍书之刊落紧语。故有是下教。而既无此虑。又有一本载在本集。则师门之意。未必在于叠录。且此本终非完本。日后全本之出。随意添入。未为不可。即今道理。忌讳碍眼者外。虽只字片言。固当收入。为录他人文字。删去紧关本文。轻重本末之义。一切倒置矣。此意并与拾遗继刊之意。备质于黄台。则一一称好。少无违咈之色。今虽作古。此心则少无歉愧于幽明矣。至于并为二字。执事之中本及箕本皆有之。以此归咎于同门。无乃反被其笑耶。初不详考原文。径发疑怒。多费辞气。殊切闷叹。此中付役时凡具粗备。虽无执事。无虑于完役。而鄙所奉请者。事系重大。本宅子弟似当来见。道理当如是。而执事不欲来见。则虽甚怅缺。亦复奈何。目录一遵箕本。执事虽来。别无更捡之事。而正本登板。难保其误字之全无。此际老成眼熟者。点捡终始。则岂不大益。而执事病昏。难办此役。则亦没奈何。望须勿费疑怒。从容熟商。回便详示去就。则人马当为治送矣。万万方赴开宁杀狱。临发胡倩。谅察望也。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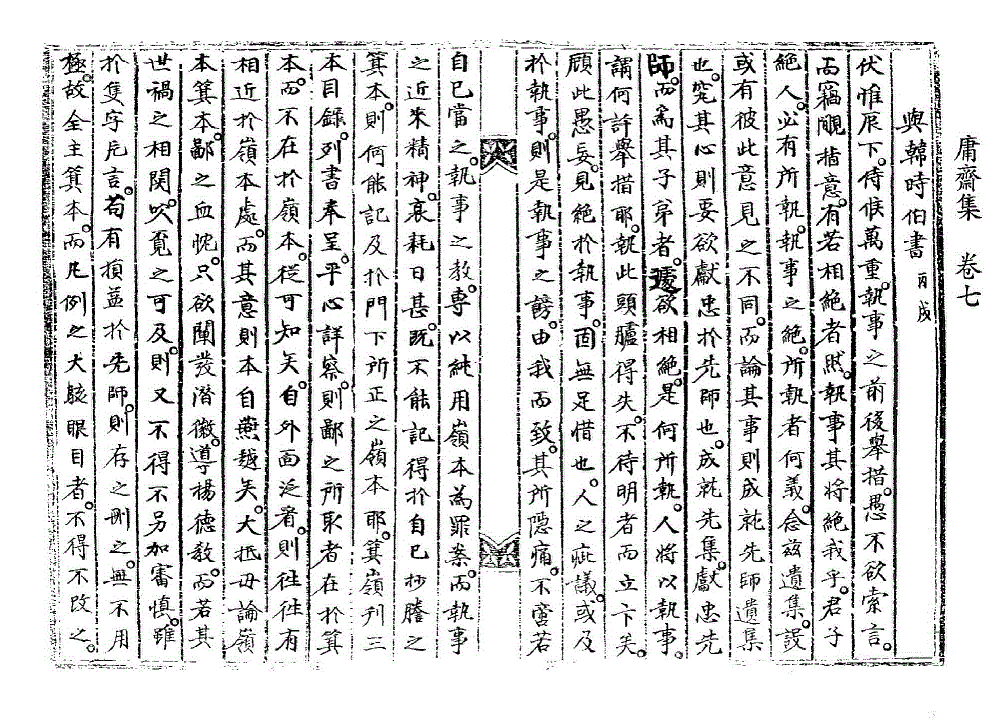 与韩时伯书(丙戌)
与韩时伯书(丙戌)伏惟辰下。侍候万重。执事之前后举措。愚不欲索言。而窃覸指意。有若相绝者然。执事其将绝我乎。君子绝人。必有所执。执事之绝。所执者何义。念玆遗集。设或有彼此意见之不同。而论其事则成就先师遗集也。究其心则要欲献忠于先师也。成就先集。献忠先师。而为其子弟者。遽欲相绝。是何所执。人将以执事。谓何许举措耶。执此头胪得失。不待明者而立卞矣。顾此愚妄。见绝于执事。固无足惜也。人之疵议。或及于执事。则是执事之谤。由我而致。其所隐痛。不啻若自己当之。执事之教。专以纯用岭本为罪案。而执事之近来精神。衰耗日甚。既不能记得于自己抄誊之箕本。则何能记及于门下所正之岭本耶。箕岭刊三本目录。列书奉呈。平心详察。则鄙之所取者在于箕本。而不在于岭本。从可知矣。自外面泛看。则往往有相近于岭本处。而其意则本自燕越矣。大抵毋论岭本箕本。鄙之血忱。只欲阐发潜徽。导扬德教。而若其世祸之相关。吹觅之可及。则又不得不另加审慎。虽于只字片言。苟有损益于先师。则存之删之。无不用极。故全主箕本。而凡例之大骇眼目者。不得不改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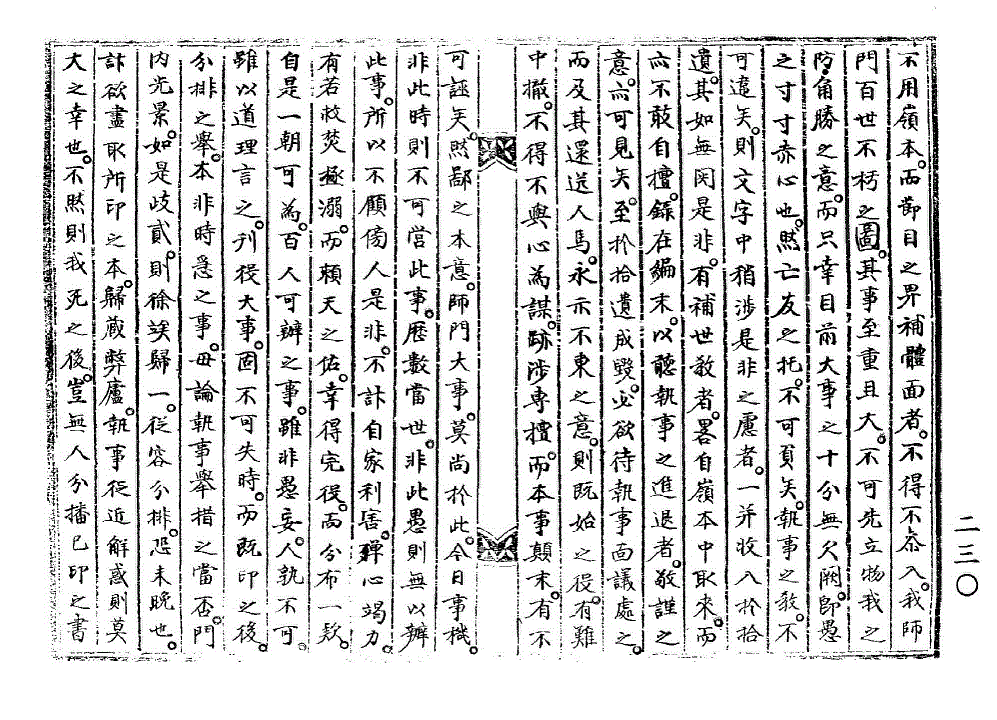 不用岭本。而节目之畀补体面者。不得不参入。我师门百世不朽之图。其事至重且大。不可先立物我之防,角胜之意。而只幸目前大事之十分无欠阙。即愚之寸寸赤心也。然亡友之托。不可负矣。执事之教。不可违矣。则文字中稍涉是非之虑者。一并收入于拾遗。其如无关是非。有补世教者。略自岭本中取来。而亦不敢自擅。录在编末。以听执事之进退者。敬谨之意。亦可见矣。至于拾遗成毁。必欲待执事面议处之。而及其还送人马。永示不东之意。则既始之役。有难中撤。不得不与心为谋。迹涉专擅。而本事颠末。有不可诬矣。然鄙之本意。师门大事。莫尚于此。今日事机。非此时则不可营此事。历数当世。非此愚则无以办此事。所以不顾傍人是非。不计自家利害。殚心竭力。有若救焚拯溺。而赖天之佑。幸得完役。而分布一款。自是一朝可为。百人可办之事。虽非愚妄。人孰不可。虽以道理言之。刊役大事。固不可失时。而既印之后。分排之举。本非时急之事。毋论执事举措之当否。门内光景。如是歧贰。则徐俟归一。从容分排。恐未晚也。计欲尽取所印之本。归藏弊庐。执事从近解惑则莫大之幸也。不然则我死之后。岂无人分播已印之书
不用岭本。而节目之畀补体面者。不得不参入。我师门百世不朽之图。其事至重且大。不可先立物我之防,角胜之意。而只幸目前大事之十分无欠阙。即愚之寸寸赤心也。然亡友之托。不可负矣。执事之教。不可违矣。则文字中稍涉是非之虑者。一并收入于拾遗。其如无关是非。有补世教者。略自岭本中取来。而亦不敢自擅。录在编末。以听执事之进退者。敬谨之意。亦可见矣。至于拾遗成毁。必欲待执事面议处之。而及其还送人马。永示不东之意。则既始之役。有难中撤。不得不与心为谋。迹涉专擅。而本事颠末。有不可诬矣。然鄙之本意。师门大事。莫尚于此。今日事机。非此时则不可营此事。历数当世。非此愚则无以办此事。所以不顾傍人是非。不计自家利害。殚心竭力。有若救焚拯溺。而赖天之佑。幸得完役。而分布一款。自是一朝可为。百人可办之事。虽非愚妄。人孰不可。虽以道理言之。刊役大事。固不可失时。而既印之后。分排之举。本非时急之事。毋论执事举措之当否。门内光景。如是歧贰。则徐俟归一。从容分排。恐未晚也。计欲尽取所印之本。归藏弊庐。执事从近解惑则莫大之幸也。不然则我死之后。岂无人分播已印之书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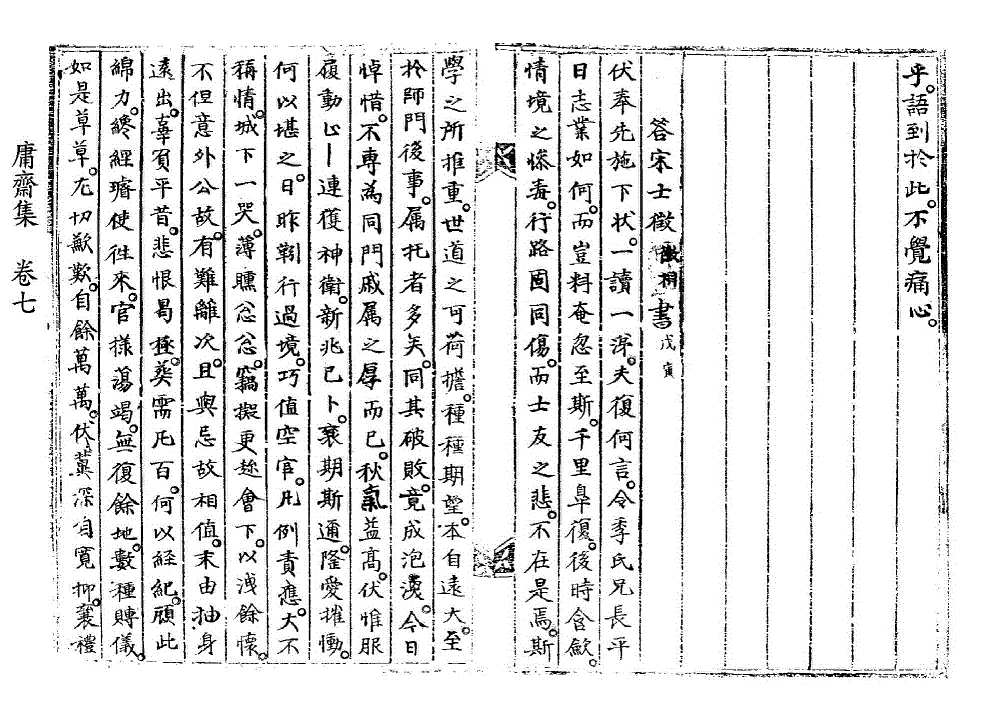 乎。语到于此。不觉痛心。
乎。语到于此。不觉痛心。答宋士徵(徵相)书(戊寅)
伏奉先施下状。一读一涕。夫复何言。令季氏兄长平日志业如何。而岂料奄忽至斯。千里皋复。后时含敛。情境之惨毒。行路固同伤。而士友之悲。不在是焉。斯学之所推重。世道之可荷担。种种期望。本自远大。至于师门后事。属托者多矣。同其破败。竟成泡涣。今日悼惜。不专为同门戚属之厚而已。秋气益高。伏惟服履动止连获神卫。新兆已卜。衰期斯迩。隆爱摧恸。何以堪之。日昨靷行过境。巧值空官。凡例责应。大不称情。城下一哭。薄曛匆匆。窃拟更趁会下。以泄馀怀。不但意外公故。有难离次。且与忌故相值。末由抽身远出。辜负平昔。悲恨曷极。葬需凡百。何以经纪。顾此绵力。才经璿使往来。官㨾荡竭。无复馀地。数种赙仪。如是草草。尤切歉叹。自馀万万。伏冀深自宽抑。襄礼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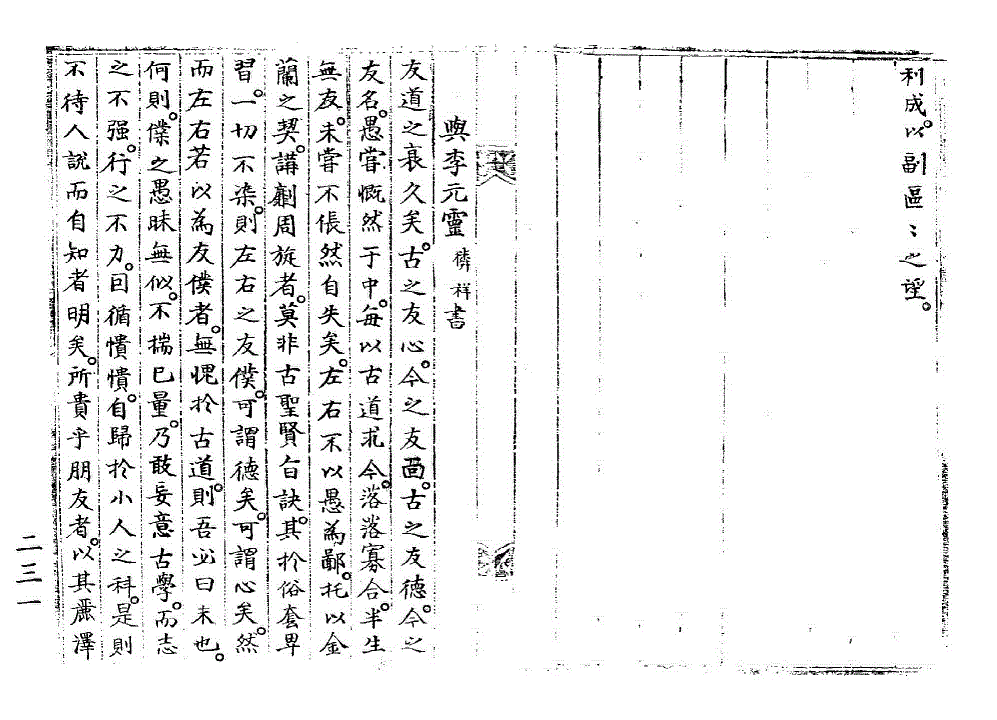 利成。以副区区之望。
利成。以副区区之望。与李元灵(獜祥)书
友道之衰久矣。古之友心。今之友面。古之友德。今之友名。愚尝慨然于中。每以古道求今。落落寡合。半生无友。未尝不伥然自失矣。左右不以愚为鄙。托以金兰之契。讲劘周旋者。莫非古圣贤旨诀。其于俗套卑习。一切不染。则左右之友仆。可谓德矣。可谓心矣。然而左右若以为友仆者。无愧于古道。则吾必曰未也。何则。仆之愚昧无似。不揣己量。乃敢妄意古学。而志之不强。行之不力。因循愦愦。自归于小人之科。是则不待人说而自知者明矣。所贵乎朋友者。以其丽泽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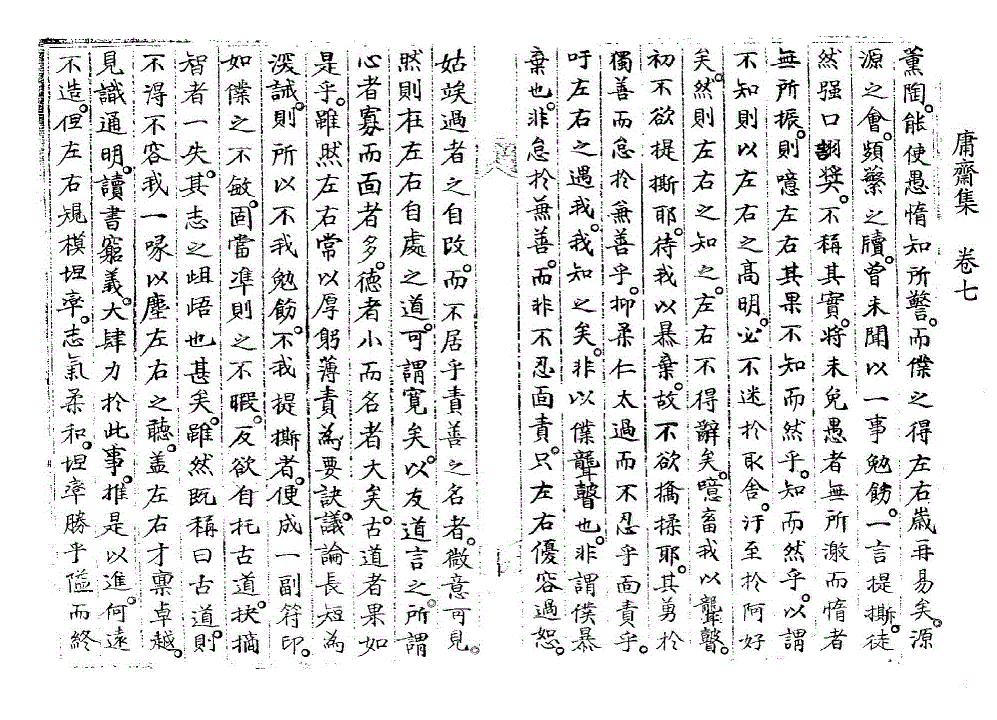 薰陶。能使愚惰知所警。而仆之得左右岁再易矣。源源之会。频蘩之牍。曾未闻以一事勉饬。一言提撕。徒然强口诩奖。不称其实。将未免愚者无所激而惰者无所振。则噫左右其果不知而然乎。知而然乎。以谓不知则以左右之高明。必不迷于取舍。污至于阿好矣。然则左右之知之。左右不得辞矣。噫畜我以聋𥌒。初不欲提撕耶。待我以暴弃。故不欲挢揉耶。其勇于独善而怠于兼善乎。抑柔仁太过而不忍乎面责乎。吁左右之遇我。我知之矣。非以仆聋𥌒也。非谓仆暴弃也。非怠于兼善。而非不忍面责。只左右优容过恕。姑俟过者之自改。而不居乎责善之名者。微意可见。然则在左右自处之道。可谓宽矣。以友道言之。所谓心者寡而面者多。德者小而名者大矣。古道者果如是乎。虽然左右常以厚躬薄责为要诀。议论长短为深诫。则所以不我勉饬。不我提撕者。便成一副符印。如仆之不敏。固当准则之不暇。反欲自托古道。抉摘智者一失。其志之龃龉也甚矣。虽然既称曰古道。则不得不容我一喙以尘左右之听。盖左右才禀卓越。见识通明。读书穷义。大肆力于此事。推是以进。何远不造。但左右规模坦率。志气柔和。坦率胜乎隘而终
薰陶。能使愚惰知所警。而仆之得左右岁再易矣。源源之会。频蘩之牍。曾未闻以一事勉饬。一言提撕。徒然强口诩奖。不称其实。将未免愚者无所激而惰者无所振。则噫左右其果不知而然乎。知而然乎。以谓不知则以左右之高明。必不迷于取舍。污至于阿好矣。然则左右之知之。左右不得辞矣。噫畜我以聋𥌒。初不欲提撕耶。待我以暴弃。故不欲挢揉耶。其勇于独善而怠于兼善乎。抑柔仁太过而不忍乎面责乎。吁左右之遇我。我知之矣。非以仆聋𥌒也。非谓仆暴弃也。非怠于兼善。而非不忍面责。只左右优容过恕。姑俟过者之自改。而不居乎责善之名者。微意可见。然则在左右自处之道。可谓宽矣。以友道言之。所谓心者寡而面者多。德者小而名者大矣。古道者果如是乎。虽然左右常以厚躬薄责为要诀。议论长短为深诫。则所以不我勉饬。不我提撕者。便成一副符印。如仆之不敏。固当准则之不暇。反欲自托古道。抉摘智者一失。其志之龃龉也甚矣。虽然既称曰古道。则不得不容我一喙以尘左右之听。盖左右才禀卓越。见识通明。读书穷义。大肆力于此事。推是以进。何远不造。但左右规模坦率。志气柔和。坦率胜乎隘而终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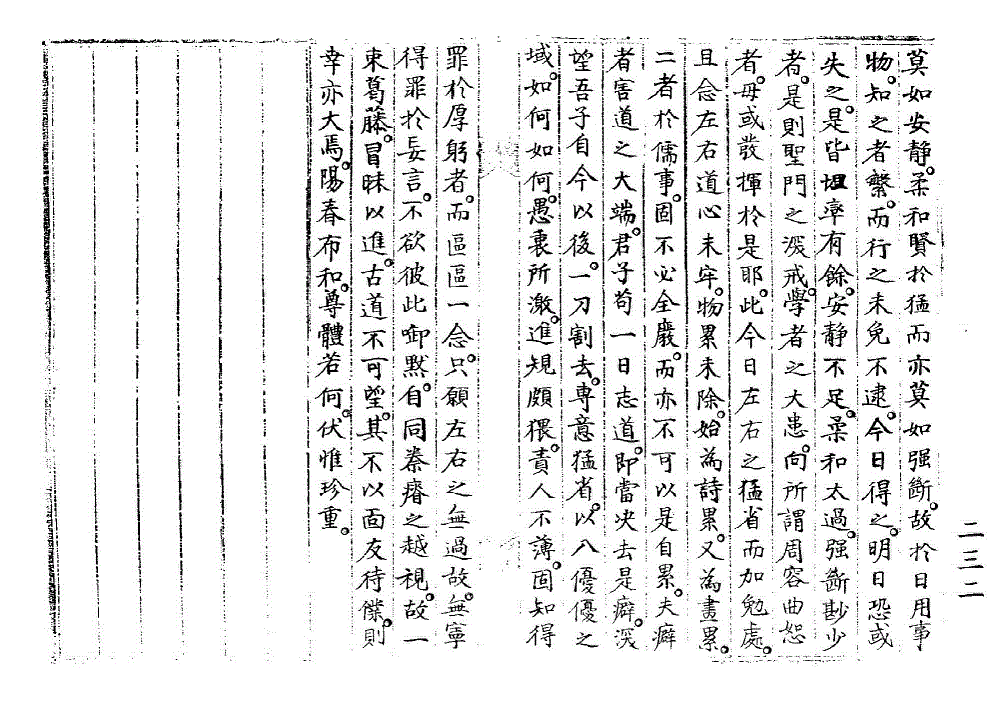 莫如安静。柔和贤于猛而亦莫如强断。故于日用事物。知之者繁。而行之未免不逮。今日得之。明日恐或失之。是皆坦率有馀。安静不足。柔和太过。强断鲜少者。是则圣门之深戒。学者之大患。向所谓周容曲恕者。毋或发挥于是耶。此今日左右之猛省而加勉处。且念左右道心未牢。物累未除。始为诗累。又为画累。二者于儒事。固不必全废。而亦不可以是自累。夫癖者害道之大端。君子苟一日志道。即当决去是癖。深望吾子自今以后。一刀割去。专意猛省。以入优优之域。如何如何。愚衷所激。进规颇猥。责人不薄。固知得罪于厚躬者。而区区一念。只愿左右之无过故。无宁得罪于妄言。不欲彼此衔默。自同秦瘠之越视。故一束葛藤。冒昧以进。古道不可望。其不以面友待仆。则幸亦大焉。阳春布和。尊体若何。伏惟珍重。
莫如安静。柔和贤于猛而亦莫如强断。故于日用事物。知之者繁。而行之未免不逮。今日得之。明日恐或失之。是皆坦率有馀。安静不足。柔和太过。强断鲜少者。是则圣门之深戒。学者之大患。向所谓周容曲恕者。毋或发挥于是耶。此今日左右之猛省而加勉处。且念左右道心未牢。物累未除。始为诗累。又为画累。二者于儒事。固不必全废。而亦不可以是自累。夫癖者害道之大端。君子苟一日志道。即当决去是癖。深望吾子自今以后。一刀割去。专意猛省。以入优优之域。如何如何。愚衷所激。进规颇猥。责人不薄。固知得罪于厚躬者。而区区一念。只愿左右之无过故。无宁得罪于妄言。不欲彼此衔默。自同秦瘠之越视。故一束葛藤。冒昧以进。古道不可望。其不以面友待仆。则幸亦大焉。阳春布和。尊体若何。伏惟珍重。答李元灵书
春寒尚峭。伏惟尊体增休。前月仆愚昧不揣。裁呈一书。自知僭妄。恭俟左右之进退。不意尊书先我。满幅郑重。忧我辅我。必欲纳之尽善无过之域。精诚所在。豚鱼可感。顾此愚蒙倘有一分知觉。则安敢不佩服遵守。来书曲折虽多。大槩不出于责人不恕论文未精。而辞直少婉。即愚者平生欲医之痼疾。况闻良友比读近思录,心经。大有操修警饬之工者乎。然则良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3L 页
 之不服也宜矣。不原其情之责。愚安敢辞乎。顾此狂妄。无地自悚。虽然来谕以为伯良非婉而告之。诱掖而鼓舞之难矣。此与愚见不同。夫责人之道。刚者抑之。使其发越之气有所屈伏。刚而复诱。则适足以增其气矣。柔者扬之。使其低微之气知所鼓舞。柔而抑之。则不足以养其气矣。黄石脱履。漂母遗饭。各因气质。权用抑扬。是乃诱人机变。不可一切以和容婉辞为不易底道理也。左右既以良友为气腾而才骏。气腾而才骏。则不可谓非强。强者其可以婉辞诱之乎。然则左右婉辞责人之教。正中愚者之病。而其于御强之道。犹有所未尽也。若其纠罪。不原其情者。可谓知良者深矣。莫非愚见之不逮。然而良友比来于变。愚未及闻知。而若以前日言议观之。则其所排攘时儒者。目之以空言无实。而所自谓实学真工。亦未见有博学慎思躬行力修之工。而兀兀穷年。孜孜不已者。只出于诗词文章之绪馀。则与其排摈时儒之义。似相矛盾矣。此非良友自厉之道。又非初学引进之义。今若曰此莫非伯良成德前事。不必提说则可。必欲为伯良规之。则其可谓不原其情乎。大抵良友之才之气超越凡类。不可与不敏者同日而语矣。愚常
之不服也宜矣。不原其情之责。愚安敢辞乎。顾此狂妄。无地自悚。虽然来谕以为伯良非婉而告之。诱掖而鼓舞之难矣。此与愚见不同。夫责人之道。刚者抑之。使其发越之气有所屈伏。刚而复诱。则适足以增其气矣。柔者扬之。使其低微之气知所鼓舞。柔而抑之。则不足以养其气矣。黄石脱履。漂母遗饭。各因气质。权用抑扬。是乃诱人机变。不可一切以和容婉辞为不易底道理也。左右既以良友为气腾而才骏。气腾而才骏。则不可谓非强。强者其可以婉辞诱之乎。然则左右婉辞责人之教。正中愚者之病。而其于御强之道。犹有所未尽也。若其纠罪。不原其情者。可谓知良者深矣。莫非愚见之不逮。然而良友比来于变。愚未及闻知。而若以前日言议观之。则其所排攘时儒者。目之以空言无实。而所自谓实学真工。亦未见有博学慎思躬行力修之工。而兀兀穷年。孜孜不已者。只出于诗词文章之绪馀。则与其排摈时儒之义。似相矛盾矣。此非良友自厉之道。又非初学引进之义。今若曰此莫非伯良成德前事。不必提说则可。必欲为伯良规之。则其可谓不原其情乎。大抵良友之才之气超越凡类。不可与不敏者同日而语矣。愚常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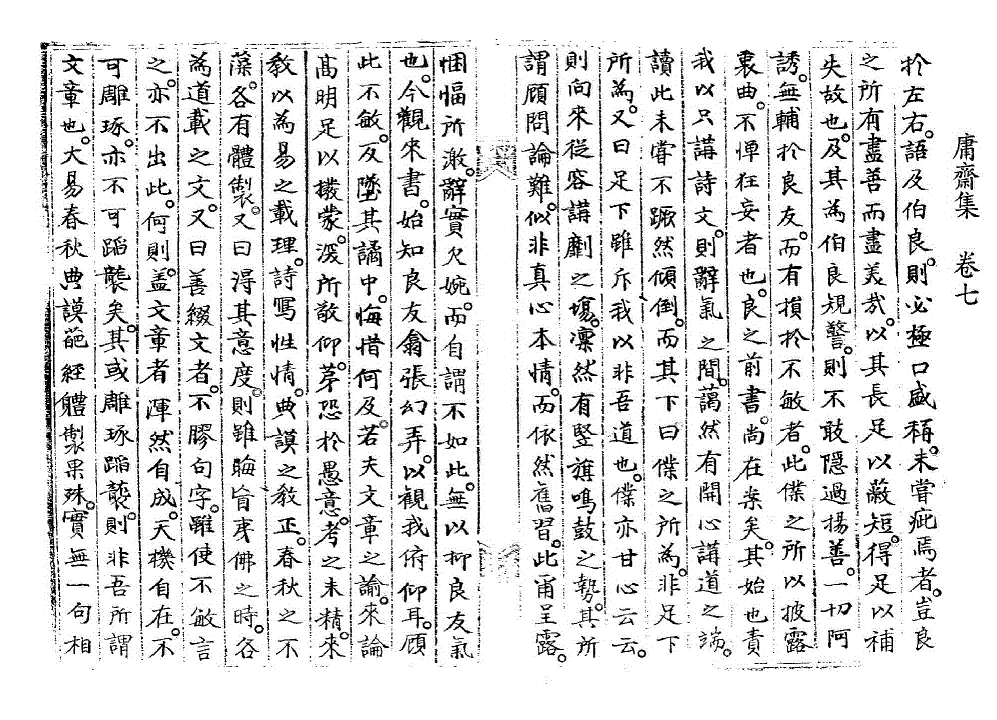 于左右。语及伯良。则必极口盛称。未尝疵焉者。岂良之所有尽善而尽美哉。以其长足以蔽短。得足以补失故也。及其为伯良规警。则不敢隐过扬善。一切阿诱。无辅于良友。而有损于不敏者。此仆之所以披露衷曲。不惮狂妄者也。良之前书。尚在案矣。其始也责我以只讲诗文。则辞气之间。蔼然有开心讲道之端。读此未尝不蹶然倾倒。而其下曰仆之所为。非足下所为。又曰足下虽斥我以非吾道也。仆亦甘心云云。则向来从容讲劘之场。凛然有竖旗鸣鼓之势。其所谓顾问论难。似非真心本情。而依然旧习。此尔呈露。悃愊所激。辞实欠婉。而自谓不如此。无以抑良友气也。今观来书。始知良友翕张幻弄。以观我俯仰耳。顾此不敏。反坠其谲中。悔惜何及。若夫文章之谕。来论高明足以拨蒙。深所敬仰。第恐于愚意。考之未精。来教以为易之载理。诗写性情。典谟之教正。春秋之不藻。各有体制。又曰得其意度。则虽晦盲夷佛之时。各为道载之文。又曰善缀文者。不胶句字。虽使不敏言之。亦不出此。何则。盖文章者浑然自成。天机自在。不可雕琢。亦不可蹈袭矣。其或雕琢蹈袭。则非吾所谓文章也。大易春秋典谟葩经体制果殊。实无一句相
于左右。语及伯良。则必极口盛称。未尝疵焉者。岂良之所有尽善而尽美哉。以其长足以蔽短。得足以补失故也。及其为伯良规警。则不敢隐过扬善。一切阿诱。无辅于良友。而有损于不敏者。此仆之所以披露衷曲。不惮狂妄者也。良之前书。尚在案矣。其始也责我以只讲诗文。则辞气之间。蔼然有开心讲道之端。读此未尝不蹶然倾倒。而其下曰仆之所为。非足下所为。又曰足下虽斥我以非吾道也。仆亦甘心云云。则向来从容讲劘之场。凛然有竖旗鸣鼓之势。其所谓顾问论难。似非真心本情。而依然旧习。此尔呈露。悃愊所激。辞实欠婉。而自谓不如此。无以抑良友气也。今观来书。始知良友翕张幻弄。以观我俯仰耳。顾此不敏。反坠其谲中。悔惜何及。若夫文章之谕。来论高明足以拨蒙。深所敬仰。第恐于愚意。考之未精。来教以为易之载理。诗写性情。典谟之教正。春秋之不藻。各有体制。又曰得其意度。则虽晦盲夷佛之时。各为道载之文。又曰善缀文者。不胶句字。虽使不敏言之。亦不出此。何则。盖文章者浑然自成。天机自在。不可雕琢。亦不可蹈袭矣。其或雕琢蹈袭。则非吾所谓文章也。大易春秋典谟葩经体制果殊。实无一句相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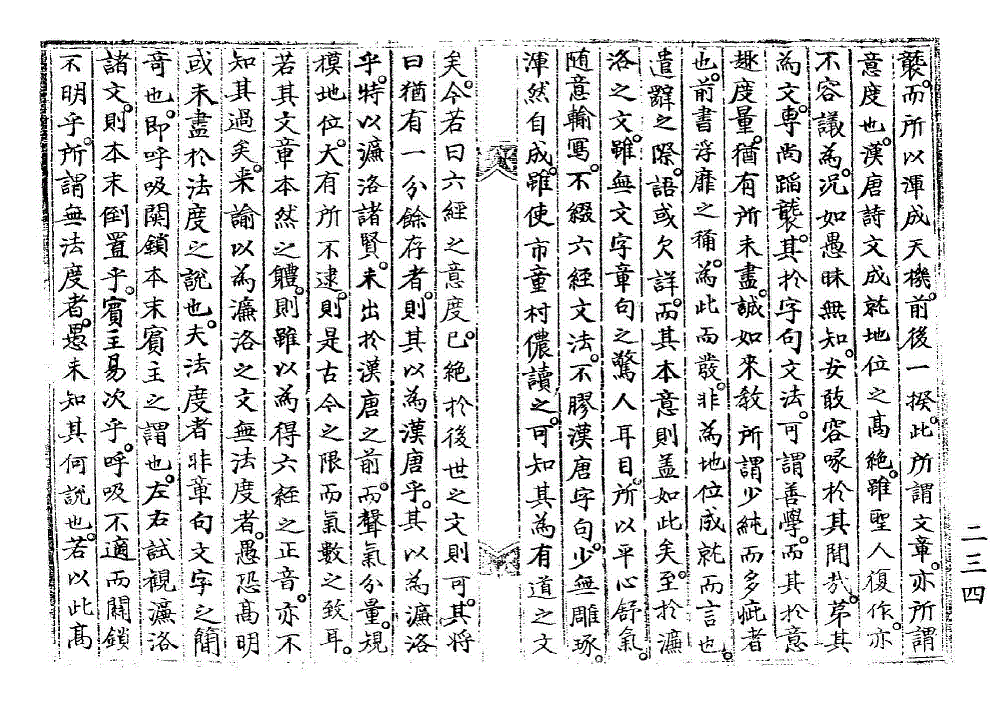 袭。而所以浑成天机。前后一揆。此所谓文章。亦所谓意度也。汉唐诗文成就地位之高绝。虽圣人复作。亦不容议为。况如愚昧无知。安敢容喙于其间哉。第其为文。专尚蹈袭。其于字句文法。可谓善学。而其于意趣度量。犹有所未尽。诚如来教所谓少纯而多疵者也。前书浮靡之称。为此而发。非为地位成就而言也。遣辞之际。语或欠详。而其本意则盖如此矣。至于濂洛之文。虽无文字章句之惊人耳目。所以平心舒气。随意输写。不缀六经文法。不胶汉唐字句。少无雕琢。浑然自成。虽使市童村侬读之。可知其为有道之文矣。今若曰六经之意度。已绝于后世之文则可。其将曰犹有一分馀存者。则其以为汉唐乎。其以为濂洛乎。特以濂洛诸贤。未出于汉唐之前。而声气分量。规模地位。大有所不逮。则是古今之限而气数之致耳。若其文章本然之体。则虽以为得六经之正音。亦不知其过矣。来谕以为濂洛之文无法度者。愚恐高明或未尽于法度之说也。夫法度者非章句文字之简奇也。即呼吸关锁本末宾主之谓也。左右试观濂洛诸文。则本末倒置乎。宾主易次乎。呼吸不适而关锁不明乎。所谓无法度者。愚未知其何说也。若以此高
袭。而所以浑成天机。前后一揆。此所谓文章。亦所谓意度也。汉唐诗文成就地位之高绝。虽圣人复作。亦不容议为。况如愚昧无知。安敢容喙于其间哉。第其为文。专尚蹈袭。其于字句文法。可谓善学。而其于意趣度量。犹有所未尽。诚如来教所谓少纯而多疵者也。前书浮靡之称。为此而发。非为地位成就而言也。遣辞之际。语或欠详。而其本意则盖如此矣。至于濂洛之文。虽无文字章句之惊人耳目。所以平心舒气。随意输写。不缀六经文法。不胶汉唐字句。少无雕琢。浑然自成。虽使市童村侬读之。可知其为有道之文矣。今若曰六经之意度。已绝于后世之文则可。其将曰犹有一分馀存者。则其以为汉唐乎。其以为濂洛乎。特以濂洛诸贤。未出于汉唐之前。而声气分量。规模地位。大有所不逮。则是古今之限而气数之致耳。若其文章本然之体。则虽以为得六经之正音。亦不知其过矣。来谕以为濂洛之文无法度者。愚恐高明或未尽于法度之说也。夫法度者非章句文字之简奇也。即呼吸关锁本末宾主之谓也。左右试观濂洛诸文。则本末倒置乎。宾主易次乎。呼吸不适而关锁不明乎。所谓无法度者。愚未知其何说也。若以此高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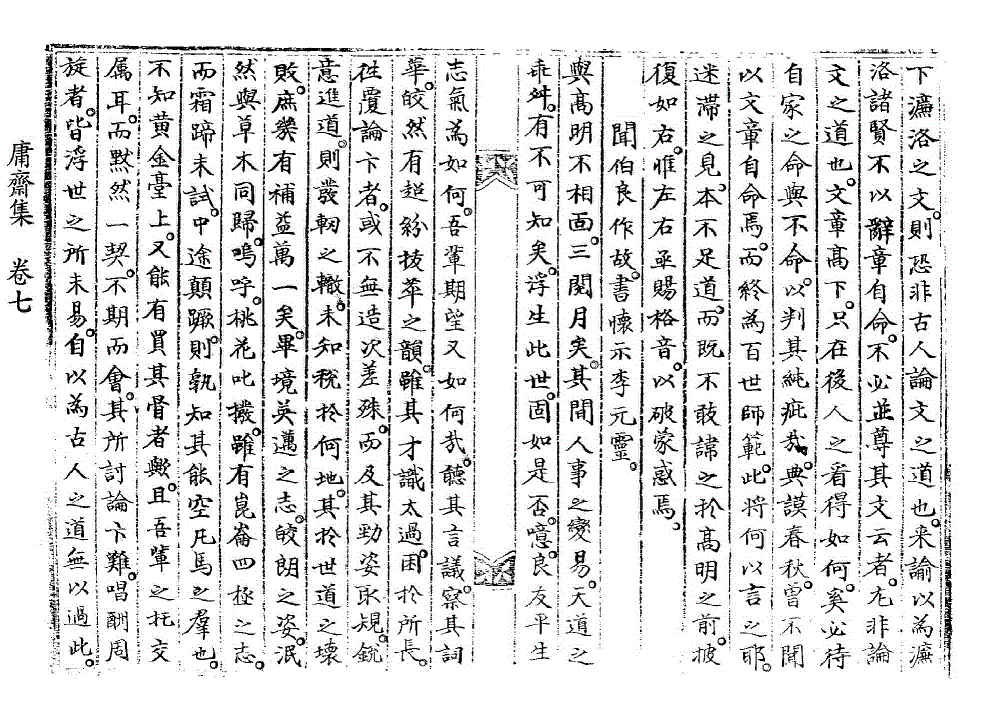 下濂洛之文。则恐非古人论文之道也。来谕以为濂洛诸贤不以辞章自命。不必并尊其文云者。尤非论文之道也。文章高下。只在后人之看得如何。奚必待自家之命与不命。以判其纯疵哉。典谟春秋。曾不闻以文章自命焉。而终为百世师范。此将何以言之耶。迷滞之见。本不足道。而既不敢讳之于高明之前。披复如右。惟左右亟赐格音。以破蒙惑焉。
下濂洛之文。则恐非古人论文之道也。来谕以为濂洛诸贤不以辞章自命。不必并尊其文云者。尤非论文之道也。文章高下。只在后人之看得如何。奚必待自家之命与不命。以判其纯疵哉。典谟春秋。曾不闻以文章自命焉。而终为百世师范。此将何以言之耶。迷滞之见。本不足道。而既不敢讳之于高明之前。披复如右。惟左右亟赐格音。以破蒙惑焉。闻伯良作故。书怀示李元灵。
与高明不相面。三阅月矣。其间人事之变易。天道之乖舛。有不可知矣。浮生此世。固如是否。噫。良友平生志气为如何。吾辈期望又如何哉。听其言议。察其词华。皎然有超纷拔萃之韵。虽其才识太过。困于所长。往覆论卞者。或不无造次差殊。而及其劲姿取规。锐意进道。则发轫之辙。未知税于何地。其于世道之坏败。庶几有补益万一矣。毕境英迈之志。皎朗之姿。泯然与草木同归。呜呼。桃花叱拨。虽有昆崙四极之志。而霜蹄未试。中途颠蹶。则孰知其能空凡马之群也。不知黄金台上。又能有买其骨者欤。且吾辈之托交属耳。而默然一契。不期而会。其所讨论卞难。唱酬周旋者。皆浮世之所未易。自以为古人之道无以过此。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5L 页
 顾自愚鲁不振。亦或有提撕警省之益矣。呜呼。千里之途未半。瞽者之相已失。仰嘘俯噫。伥伥然迷所之矣。使良友至此者。命耶数耶。抑斯世之不幸耶。抑吾辈之福薄耶。呜呼。三代之和气浇漓久矣。世之有一艺一能者。皆未得保其善养。则良也之才之能。亦安得独脱其大化。与龌龊辈同其寿福耶。日月易迈。大诀不远。湖山阻绝。莫以致躬。临绋一哭。亦未如意。山窗静夜。只自掩泣沾巾而已。凡今之人。孰知我悲。惟元灵知之。玆以及之。
顾自愚鲁不振。亦或有提撕警省之益矣。呜呼。千里之途未半。瞽者之相已失。仰嘘俯噫。伥伥然迷所之矣。使良友至此者。命耶数耶。抑斯世之不幸耶。抑吾辈之福薄耶。呜呼。三代之和气浇漓久矣。世之有一艺一能者。皆未得保其善养。则良也之才之能。亦安得独脱其大化。与龌龊辈同其寿福耶。日月易迈。大诀不远。湖山阻绝。莫以致躬。临绋一哭。亦未如意。山窗静夜。只自掩泣沾巾而已。凡今之人。孰知我悲。惟元灵知之。玆以及之。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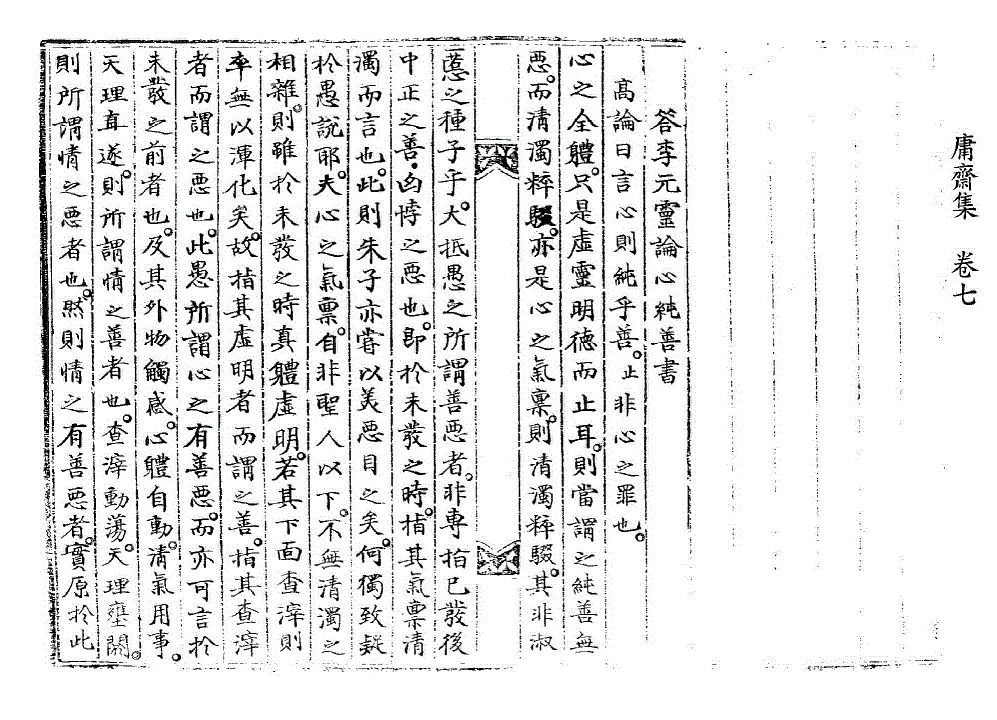 答李元灵论心纯善书
答李元灵论心纯善书高论曰言心则纯乎善(止)非心之罪也。
心之全体。只是虚灵明德而止耳。则当谓之纯善无恶。而清浊粹驳。亦是心之气禀。则清浊粹驳。其非淑慝之种子乎。大抵愚之所谓善恶者。非专指已发后中正之善,凶悖之恶也。即于未发之时。指其气禀清浊而言也。此则朱子亦尝以美恶目之矣。何独致疑于愚说耶。夫心之气禀。自非圣人以下。不无清浊之相杂。则虽于未发之时真体虚明。若其下面查滓则卒无以浑化矣。故指其虚明者而谓之善。指其查滓者而谓之恶也。此愚所谓心之有善恶。而亦可言于未发之前者也。及其外物触感。心体自动。清气用事。天理直遂。则所谓情之善者也。查滓动荡。天理壅阏。则所谓情之恶者也。然则情之有善恶者。实原于此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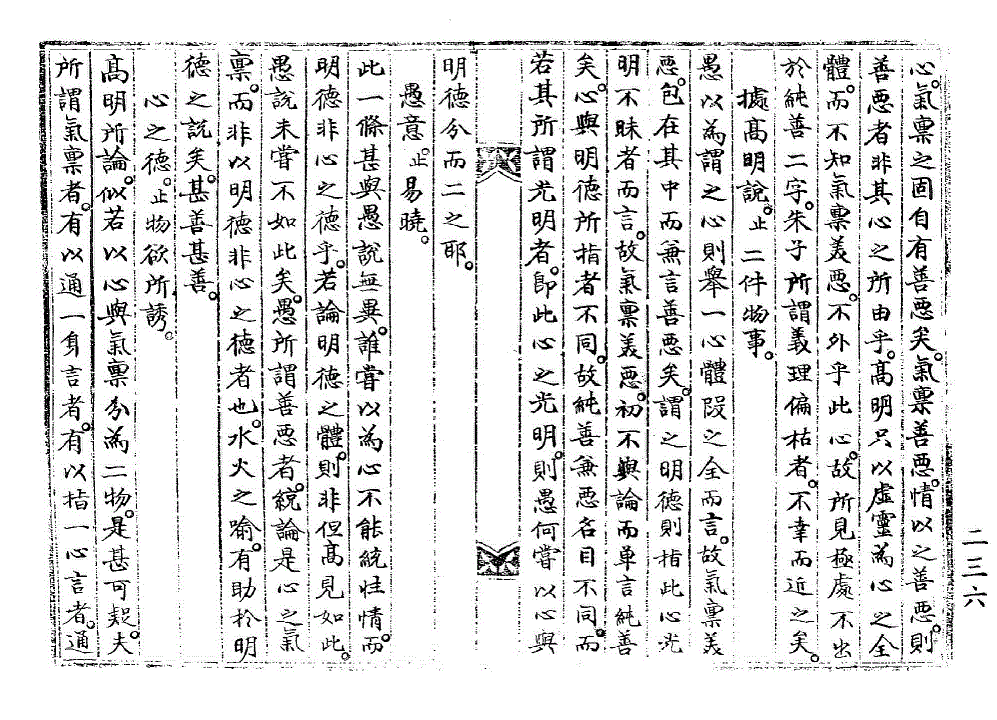 心。气禀之固自有善恶矣。气禀善恶。情以之善恶。则善恶者非其心之所由乎。高明只以虚灵为心之全体。而不知气禀美恶。不外乎此心。故所见极处不出于纯善二字。朱子所谓义理偏枯者。不幸而近之矣。
心。气禀之固自有善恶矣。气禀善恶。情以之善恶。则善恶者非其心之所由乎。高明只以虚灵为心之全体。而不知气禀美恶。不外乎此心。故所见极处不出于纯善二字。朱子所谓义理偏枯者。不幸而近之矣。据高明说(止)二件物事。
愚以为谓之心则举一心体段之全而言。故气禀美恶。包在其中而兼言善恶矣。谓之明德则指此心光明不昧者而言。故气禀美恶。初不与论而单言纯善矣。心与明德所指者不同。故纯善兼恶名目不同。而若其所谓光明者。即此心之光明。则愚何尝以心与明德分而二之耶。
愚意(止)易晓。
此一条甚与愚说无异。谁尝以为心不能统性情。而明德非心之德乎。若论明德之体。则非但高见如此。愚说未尝不如此矣。愚所谓善恶者。统论是心之气禀。而非以明德非心之德者也。水火之喻。有助于明德之说矣。甚善甚善。
心之德(止)物欲所诱。
高明所论。似若以心与气禀分为二物。是甚可疑。夫所谓气禀者。有以通一身言者。有以指一心言者。通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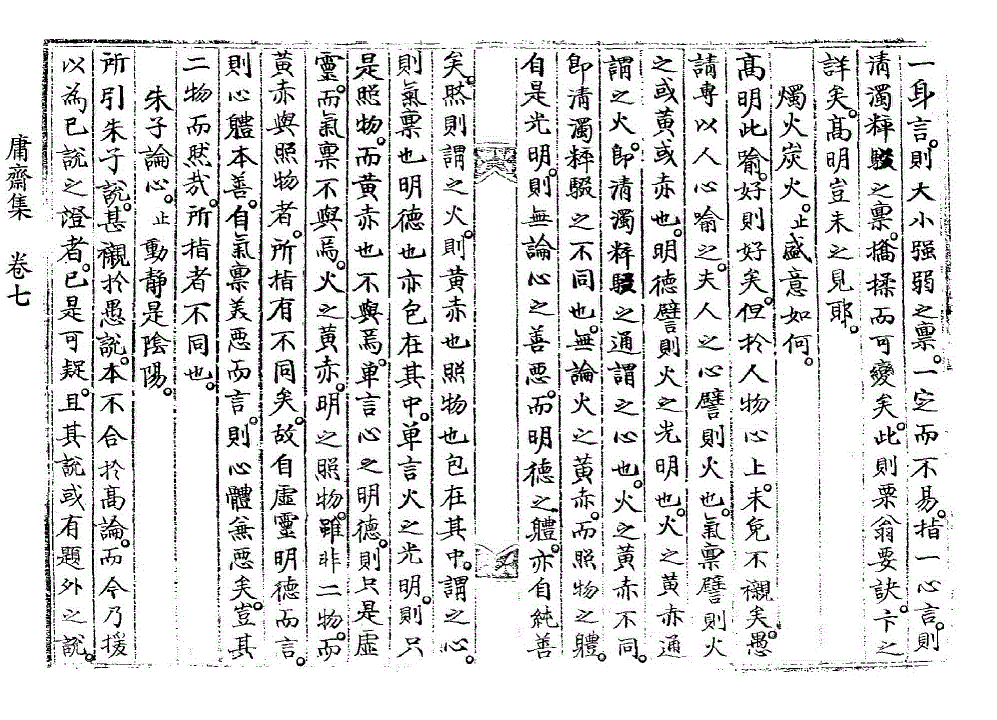 一身言。则大小强弱之禀。一定而不易。指一心言。则清浊粹驳之禀。挢揉而可变矣。此则栗翁要诀。卞之详矣。高明岂未之见耶。
一身言。则大小强弱之禀。一定而不易。指一心言。则清浊粹驳之禀。挢揉而可变矣。此则栗翁要诀。卞之详矣。高明岂未之见耶。烛火炭火(止)盛意如何。
高明此喻。好则好矣。但于人物心上。未免不衬矣。愚请专以人心喻之。夫人之心譬则火也。气禀譬则火之或黄或赤也。明德譬则火之光明也。火之黄赤通谓之火。即清浊粹驳之通谓之心也。火之黄赤不同。即清浊粹驳之不同也。无论火之黄赤。而照物之体。自是光明。则无论心之善恶。而明德之体。亦自纯善矣。然则谓之火。则黄赤也照物也包在其中。谓之心。则气禀也明德也亦包在其中。单言火之光明。则只是照物。而黄赤也不与焉。单言心之明德。则只是虚灵。而气禀不与焉。火之黄赤。明之照物。虽非二物。而黄赤与照物者。所指有不同矣。故自虚灵明德而言。则心体本善。自气禀美恶而言。则心体兼恶矣。岂其二物而然哉。所指者不同也。
朱子论心(止)动静是阴阳。
所引朱子说。甚衬于愚说。本不合于高论。而今乃援以为己说之證者。已是可疑。且其说或有题外之说。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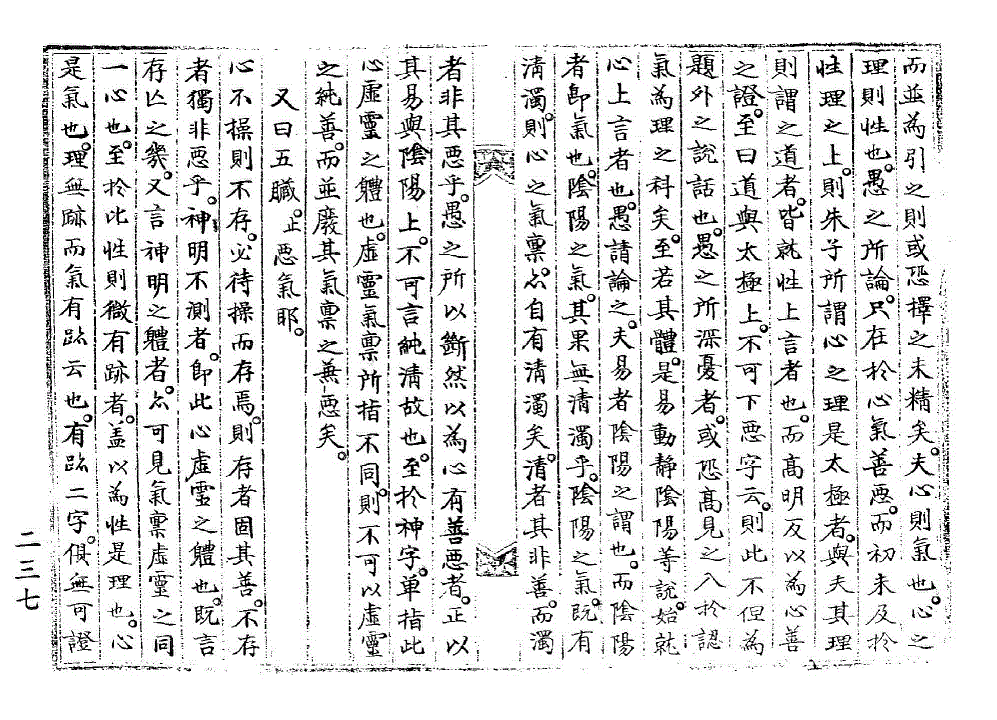 而并为引之则或恐择之未精矣。夫心则气也。心之理则性也。愚之所论。只在于心气善恶。而初未及于性理之上。则朱子所谓心之理是太极者。与夫其理则谓之道者。皆就性上言者也。而高明反以为心善之證。至曰道与太极上。不可下恶字云。则此不但为题外之说话也。愚之所深忧者。或恐高见之入于认气为理之科矣。至若其体。是易动静阴阳等说。始就心上言者也。愚请论之。夫易者阴阳之谓也。而阴阳者即气也。阴阳之气。其果无清浊乎。阴阳之气。既有清浊。则心之气禀。亦自有清浊矣。清者其非善。而浊者非其恶乎。愚之所以断然以为心有善恶者。正以其易与阴阳上。不可言纯清故也。至于神字。单指此心虚灵之体也。虚灵气禀所指不同。则不可以虚灵之纯善。而并废其气禀之兼恶矣。
而并为引之则或恐择之未精矣。夫心则气也。心之理则性也。愚之所论。只在于心气善恶。而初未及于性理之上。则朱子所谓心之理是太极者。与夫其理则谓之道者。皆就性上言者也。而高明反以为心善之證。至曰道与太极上。不可下恶字云。则此不但为题外之说话也。愚之所深忧者。或恐高见之入于认气为理之科矣。至若其体。是易动静阴阳等说。始就心上言者也。愚请论之。夫易者阴阳之谓也。而阴阳者即气也。阴阳之气。其果无清浊乎。阴阳之气。既有清浊。则心之气禀。亦自有清浊矣。清者其非善。而浊者非其恶乎。愚之所以断然以为心有善恶者。正以其易与阴阳上。不可言纯清故也。至于神字。单指此心虚灵之体也。虚灵气禀所指不同。则不可以虚灵之纯善。而并废其气禀之兼恶矣。又曰五脏(止)恶气耶。
心不操则不存。必待操而存焉。则存者固其善。不存者独非恶乎。神明不测者。即此心虚灵之体也。既言存亡之几。又言神明之体者。亦可见气禀虚灵之同一心也。至于比性则微有迹者。盖以为性是理也。心是气也。理无迹而气有迹云也。有迹二字。俱无可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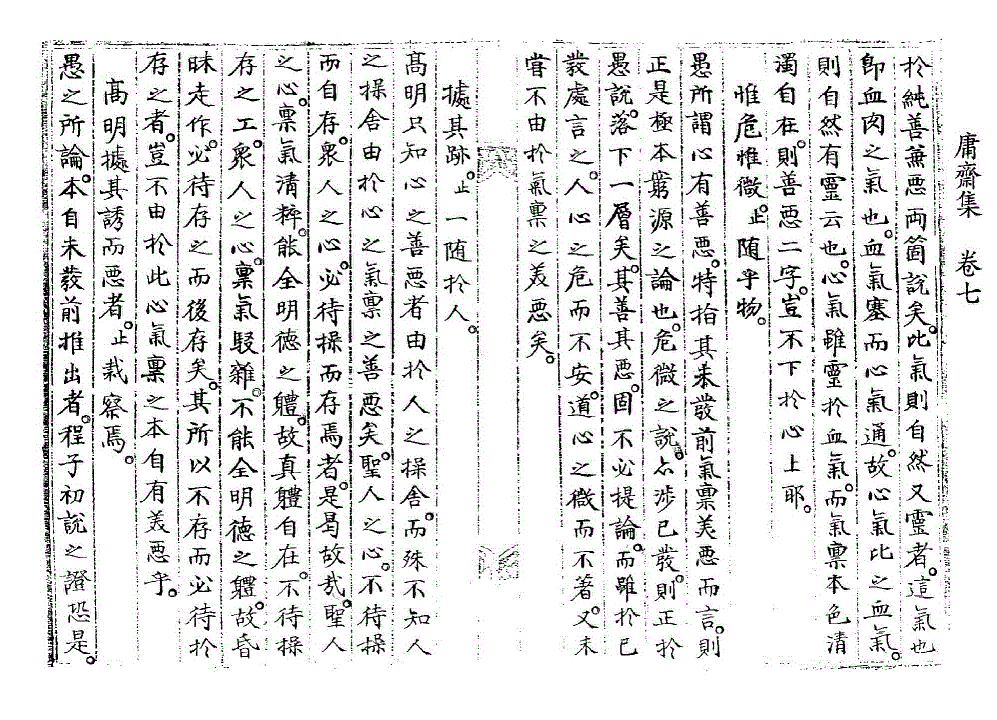 于纯善兼恶两个说矣。比气则自然又灵者。这气也即血肉之气也。血气塞而心气通。故心气比之血气。则自然有灵云也。心气虽灵于血气。而气禀本色清浊自在。则善恶二字。岂不下于心上耶。
于纯善兼恶两个说矣。比气则自然又灵者。这气也即血肉之气也。血气塞而心气通。故心气比之血气。则自然有灵云也。心气虽灵于血气。而气禀本色清浊自在。则善恶二字。岂不下于心上耶。惟危惟微(止)随乎物。
愚所谓心有善恶。特指其未发前气禀美恶而言。则正是极本穷源之论也。危微之说。亦涉已发。则正于愚说。落下一层矣。其善其恶。固不必提论。而虽于已发处言之。人心之危而不安。道心之微而不著。又未尝不由于气禀之美恶矣。
据其迹(止)一随于人。
高明只知心之善恶者由于人之操舍。而殊不知人之操舍由于心之气禀之善恶矣。圣人之心。不待操而自存。众人之心。必待操而存焉者。是曷故哉。圣人之心。禀气清粹。能全明德之体。故真体自在。不待操存之工。众人之心。禀气驳杂。不能全明德之体。故昏昧走作。必待存之而后存矣。其所以不存而必待于存之者。岂不由于此心气禀之本自有美恶乎。
高明据其诱而恶者(止)裁察焉。
愚之所论。本自未发前推出者。程子初说之證恐是。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8L 页
 高明未得说者之本旨矣。
高明未得说者之本旨矣。总论
心之纯善兼恶之说。其本盖在于心与气禀同异之分矣。高明曰心之德本善。而用时有恶者。拘于气禀而然也。此则以心与气禀分为二物也。愚以为心之明德虽善。而心之气禀有善恶。此则以心与气禀合为一物也。苟能明卞乎此。则心之善恶者。不待卞说而自解矣。夫人之方寸。一而已矣。而方寸中所贮之气即心也。愚以为气禀者。只在方寸之中。则即此气禀。通谓之心也。气禀本色清浊自在。则即此清浊通谓之善恶矣。不知高明以气禀谓在方寸之中乎。抑谓在方寸之外乎。若谓在方寸之外。则心与气禀。既有内外之分矣。此心发时。气禀必自百体上超入矣。此则嵬岩所谓退听用事之说。而强卞屡屈。文案昭然。高明固已洞察而深排。则愚固知高明必不甘心于同归矣。若以谓同在方寸之中。而指其虚灵者曰心也。指其不齐者曰气禀也。则语意径庭。尤未妥贴。夫方寸一心。心一方寸。宁有一方寸之中。或心而或非心者乎。此等界分。本不难晓。望须明着眼目。猛着精神。期于归一。千万幸甚。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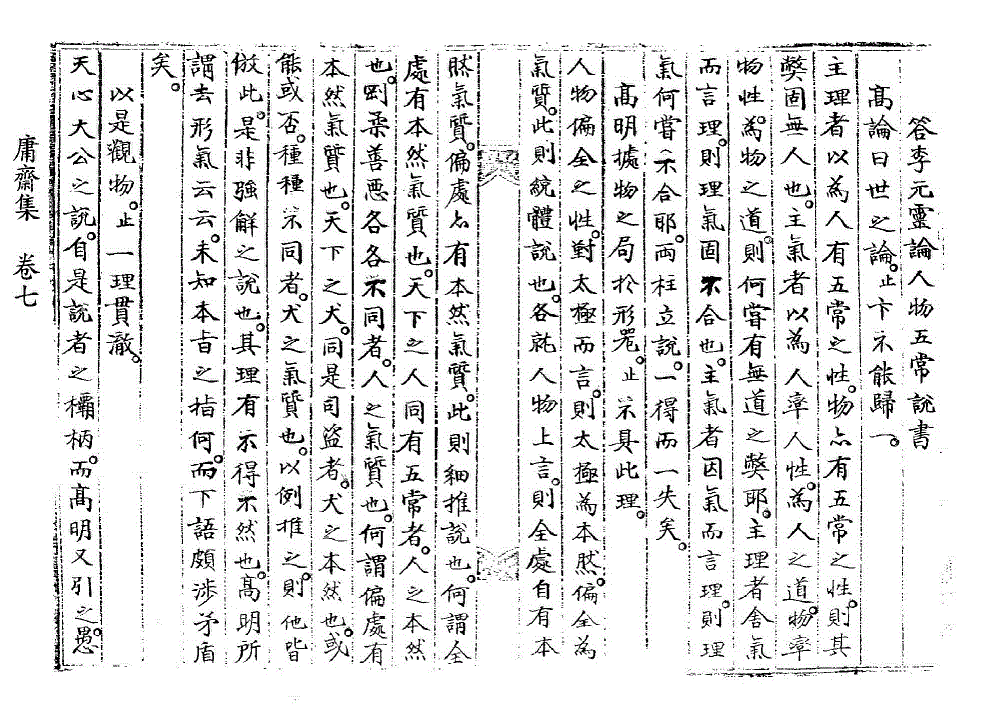 答李元灵论人物五常说书
答李元灵论人物五常说书高论曰世之论(止)卞不能归一。
主理者以为人有五常之性。物亦有五常之性。则其弊固无人也。主气者以为人率人性。为人之道。物率物性。为物之道。则何尝有无道之弊耶。主理者舍气而言理。则理气固不合也。主气者因气而言理。则理气何尝不合耶。两柱立说。一得而一失矣。
高明据物之局于形器(止)不具此理。
人物偏全之性。对太极而言。则太极为本然。偏全为气质。此则统体说也。各就人物上言。则全处自有本然气质。偏处亦有本然气质。此则细推说也。何谓全处有本然气质也。天下之人同有五常者。人之本然也。刚柔善恶各各不同者。人之气质也。何谓偏处有本然气质也。天下之犬。同是司盗者。犬之本然也。或能或否。种种不同者。犬之气质也。以例推之。则他皆仿此。是非强解之说也。其理有不得不然也。高明所谓去形气云云。未知本旨之指何。而下语颇涉矛盾矣。
以是观物(止)一理贯澈。
天心大公之说。自是说者之把柄。而高明又引之。愚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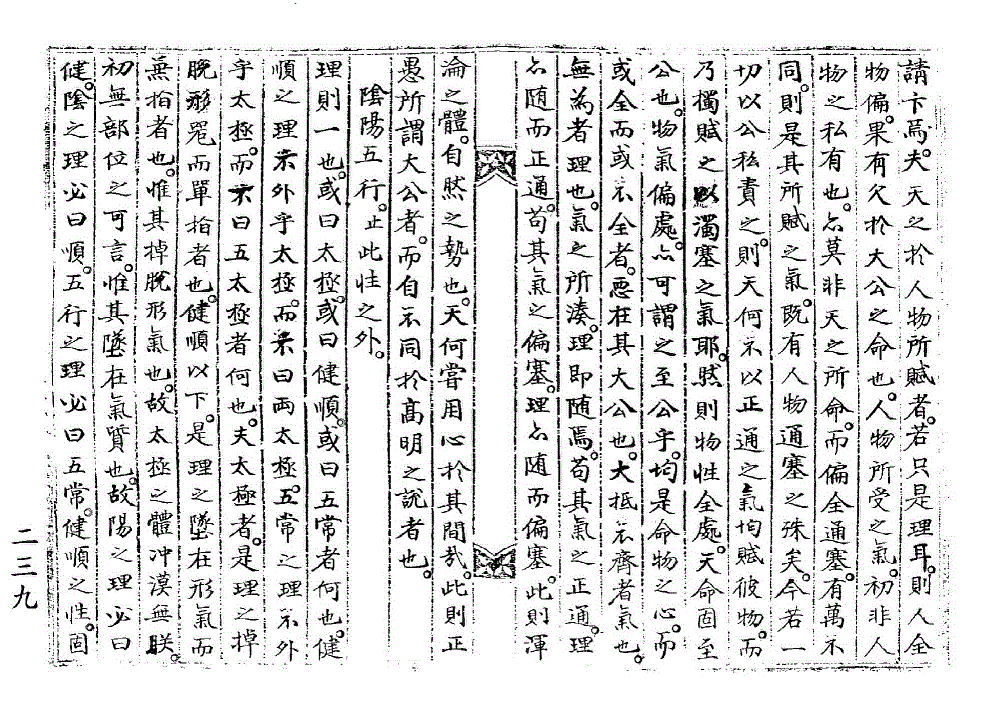 请卞焉。夫天之于人物所赋者。若只是理耳。则人全物偏。果有欠于大公之命也。人物所受之气。初非人物之私有也。亦莫非天之所命。而偏全通塞。有万不同。则是其所赋之气。既有人物通塞之殊矣。今若一切以公私责之。则天何不以正通之气均赋彼物。而乃独赋之以浊塞之气耶。然则物性全处。天命固至公也。物气偏处。亦可谓之至公乎。均是命物之心。而或全而或不全者。恶在其大公也。大抵不齐者气也。无为者理也。气之所凑。理即随焉。苟其气之正通。理亦随而正通。苟其气之偏塞。理亦随而偏塞。此则浑沦之体。自然之势也。天何尝用心于其间哉。此则正愚所谓大公者。而自不同于高明之说者也。
请卞焉。夫天之于人物所赋者。若只是理耳。则人全物偏。果有欠于大公之命也。人物所受之气。初非人物之私有也。亦莫非天之所命。而偏全通塞。有万不同。则是其所赋之气。既有人物通塞之殊矣。今若一切以公私责之。则天何不以正通之气均赋彼物。而乃独赋之以浊塞之气耶。然则物性全处。天命固至公也。物气偏处。亦可谓之至公乎。均是命物之心。而或全而或不全者。恶在其大公也。大抵不齐者气也。无为者理也。气之所凑。理即随焉。苟其气之正通。理亦随而正通。苟其气之偏塞。理亦随而偏塞。此则浑沦之体。自然之势也。天何尝用心于其间哉。此则正愚所谓大公者。而自不同于高明之说者也。阴阳五行(止)此性之外。
理则一也。或曰太极。或曰健顺。或曰五常者何也。健顺之理不外乎太极。而不曰两太极。五常之理不外乎太极。而不曰五太极者何也。夫太极者。是理之掉脱形器而单指者也。健顺以下。是理之坠在形气而兼指者也。惟其掉脱形气也。故太极之体冲漠无眹。初无部位之可言。惟其坠在气质也。故阳之理必曰健。阴之理必曰顺。五行之理必曰五常。健顺之性。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0H 页
 不外乎太极。而不曰健顺而直谓之太极。则阴阳之体。无以著矣。五常之性。固不外乎太极。而不曰五常而直谓之太极。则五气之殊。无以见矣。然则太极分为健顺。而其于一健一顺。则太极之体。无复全矣。健顺分为五常。而其于或仁或礼。则健顺之体。无复全矣。故健顺之性。对太极而言。则太极全而健顺偏矣。五常之性。对健顺而言。则健顺全而五常偏矣。性理偏全之分。已见于太极阴阳之上。则况乎吾人与物之形体既立。知觉异用之后者乎。高论中种种题目。颇欠曲折源委。更加商量如何。
不外乎太极。而不曰健顺而直谓之太极。则阴阳之体。无以著矣。五常之性。固不外乎太极。而不曰五常而直谓之太极。则五气之殊。无以见矣。然则太极分为健顺。而其于一健一顺。则太极之体。无复全矣。健顺分为五常。而其于或仁或礼。则健顺之体。无复全矣。故健顺之性。对太极而言。则太极全而健顺偏矣。五常之性。对健顺而言。则健顺全而五常偏矣。性理偏全之分。已见于太极阴阳之上。则况乎吾人与物之形体既立。知觉异用之后者乎。高论中种种题目。颇欠曲折源委。更加商量如何。一气之中(止)二命二性。
理气之体。自其一原而言。则气有偏而理自全。气有塞而理自通。自其异体而言。则气之偏塞而理亦偏塞。气之全通而理亦全通。未有气全而理偏。亦未有气塞而理通。人物之性。当论于异体之后。则人气全处人性全矣。物气偏处物性偏矣。若以为物气偏塞而物性全通。则是理气之间。判然于异体之后者也。岂其然哉。且命者天所授也。性者物所受也。自造化继善而言。则天命一也。所谓一原也。自禀赋各定而言。则物性万矣。所谓异体也。大抵高明每以人物异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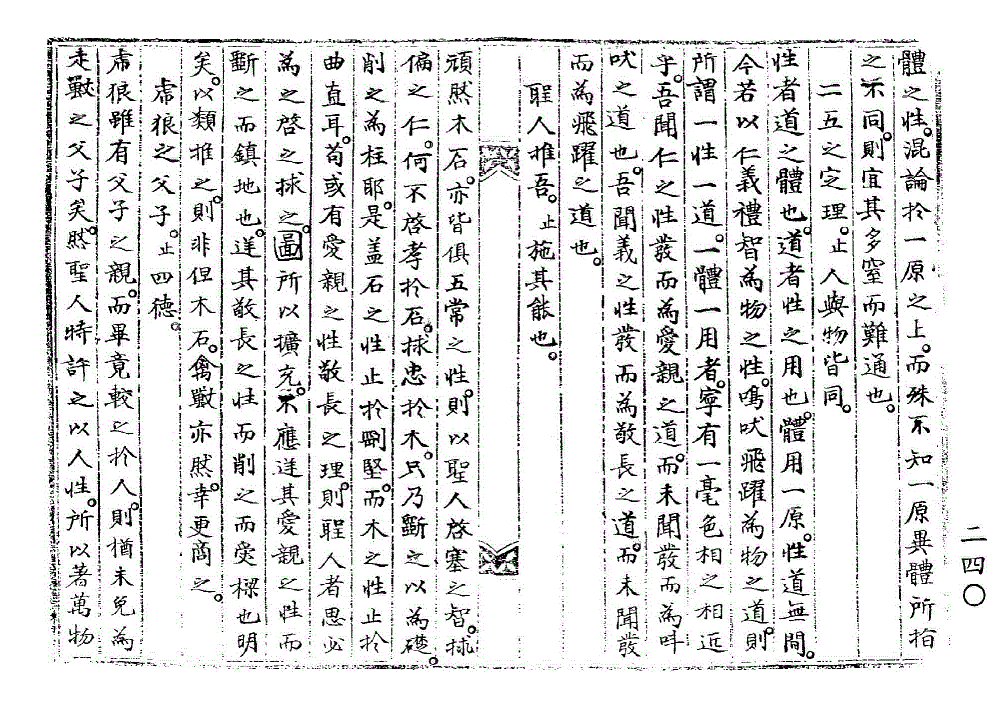 体之性。混论于一原之上。而殊不知一原异体所指之不同。则宜其多窒而难通也。
体之性。混论于一原之上。而殊不知一原异体所指之不同。则宜其多窒而难通也。二五之定理(止)人与物皆同。
性者道之体也。道者性之用也。体用一原。性道无间。今若以仁义礼智为物之性。鸣吠飞跃为物之道。则所谓一性一道。一体一用者。宁有一毫色相之相近乎。吾闻仁之性发而为爱亲之道。而未闻发而为叫吠之道也。吾闻义之性发而为敬长之道。而未闻发而为飞跃之道也。
圣人推吾(止)施其能也。
顽然木石。亦皆俱五常之性。则以圣人启塞之智。救偏之仁。何不启孝于石。救忠于木。只乃斲之以为础。削之为柱耶。是盖石之性止于刚坚。而木之性止于曲直耳。苟或有爱亲之性敬长之理。则圣人者思必为之启之救之。图所以扩充。不应逆其爱亲之性而斲之而镇地也。逆其敬长之性而削之而受梁也明矣。以类推之。则非但木石。禽兽亦然。幸更商之。
虎狼之父子(止)四德。
虎狼虽有父子之亲。而毕竟较之于人。则犹未免为走兽之父子矣。然圣人特许之以人性。所以著万物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1H 页
 同原之理也。然五常之名义最重。彼物之形气最偏。则圣人只许其一性。而不敢并许其五性者。亦以见万物异体之性也。此所谓同中自有所异。异中自有所同者也。圣人之所不许。今人欲许之。其亦难矣。
同原之理也。然五常之名义最重。彼物之形气最偏。则圣人只许其一性。而不敢并许其五性者。亦以见万物异体之性也。此所谓同中自有所异。异中自有所同者也。圣人之所不许。今人欲许之。其亦难矣。虎狼多受金气(止)信者。
虎虽多金气。而金气塞而木气通。故仁之性通焉。鸡虽多木气。而木气塞而土气通。故信之性通焉。物性通塞。只在其气之通塞。而高明欲以多寡论之。无乃错乎。
禽兽之仁义(止)以状仁信。
獜凤龟龙。不能全具五常。虎狼鸡犬。初非全无五性者。若举其一性微通者而言之。则虎仁鸡信。即目而易见矣。何必远求诸獜凤乎。
浊气之赋于物(止)其为性则一也。
种种推说论气处信好。而论性处未稳。幸更商之。
事理中节(止)有形之物。
五常名目。粹然至善。初无两等界分。而高明以事理中节者。属诸人分。以取名五气者。属之物边。中节与取名。其果为二事乎。夫仁义礼智。虽是五气之理。而其为名则本就人分上说也。朱子所谓五行之神。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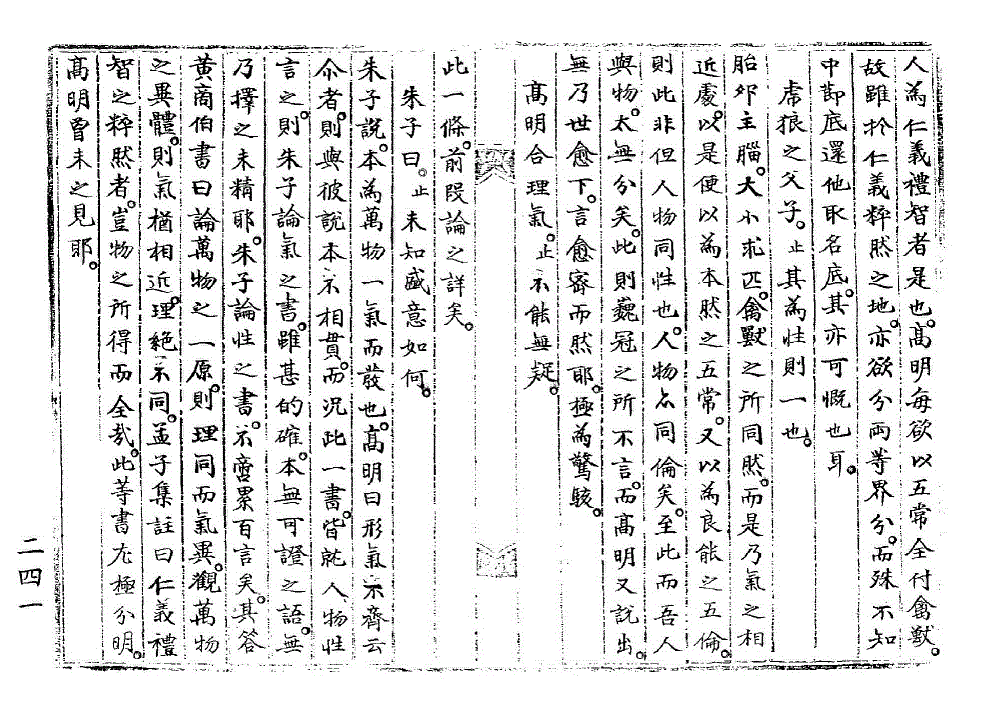 人为仁义礼智者是也。高明每欲以五常全付禽兽。故虽于仁义粹然之地。亦欲分两等界分。而殊不知中节底还他取名底。其亦可慨也耳。
人为仁义礼智者是也。高明每欲以五常全付禽兽。故虽于仁义粹然之地。亦欲分两等界分。而殊不知中节底还他取名底。其亦可慨也耳。虎狼之父子(止)其为性则一也。
胎卵主脑。大小求匹。禽兽之所同然。而是乃气之相近处。以是便以为本然之五常。又以为良能之五伦。则此非但人物同性也。人物亦同伦矣。至此而吾人与物。太无分矣。此则巍冠之所不言。而高明又说出。无乃世愈下。言愈密而然耶。极为惊骇。
高明合理气(止)不能无疑。
此一条。前段论之详矣。
朱子曰(止)未知盛意如何。
朱子说。本为万物一气而发也。高明曰形气不齐云尔者。则与彼说本不相贯。而况此一书。皆就人物性言之。则朱子论气之书。虽甚的确。本无可證之语。无乃择之未精耶。朱子论性之书。不啻累百言矣。其答黄商伯书曰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理绝不同。孟子集注曰仁义礼智之粹然者。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等书尤极分明。高明曾未之见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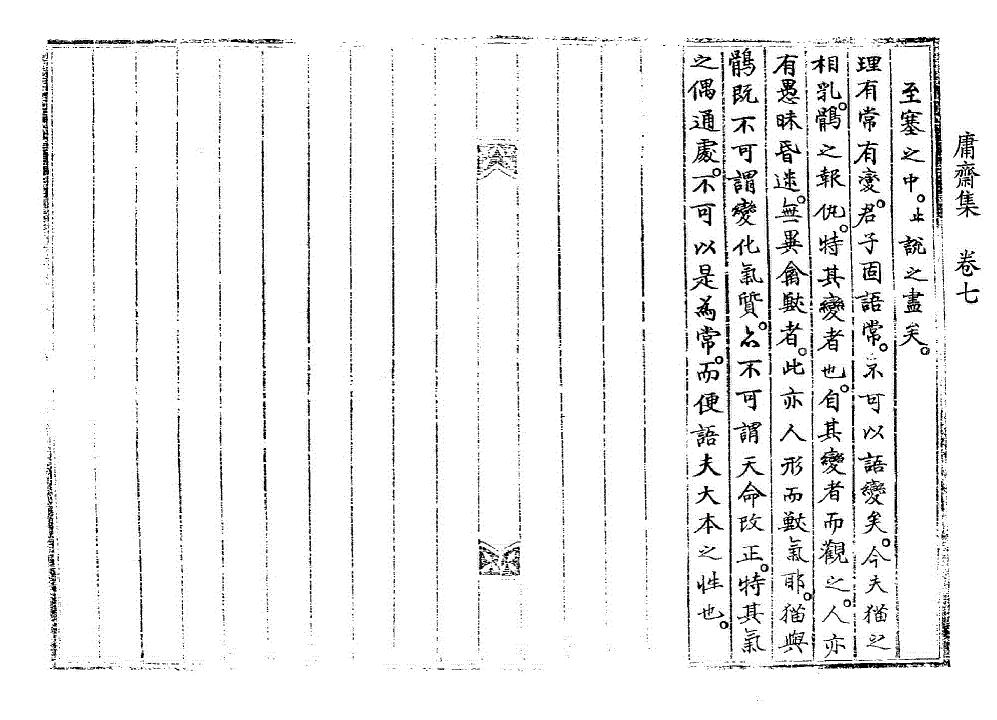 至塞之中(止)说之尽矣。
至塞之中(止)说之尽矣。理有常有变。君子固语常。不可以语变矣。今夫猫之相乳。鹘之报仇。特其变者也。自其变者而观之。人亦有愚昧昏迷。无异禽兽者。此亦人形而兽气耶。猫与鹘既不可谓变化气质。亦不可谓天命改正。特其气之偶通处。不可以是为常。而便语夫大本之性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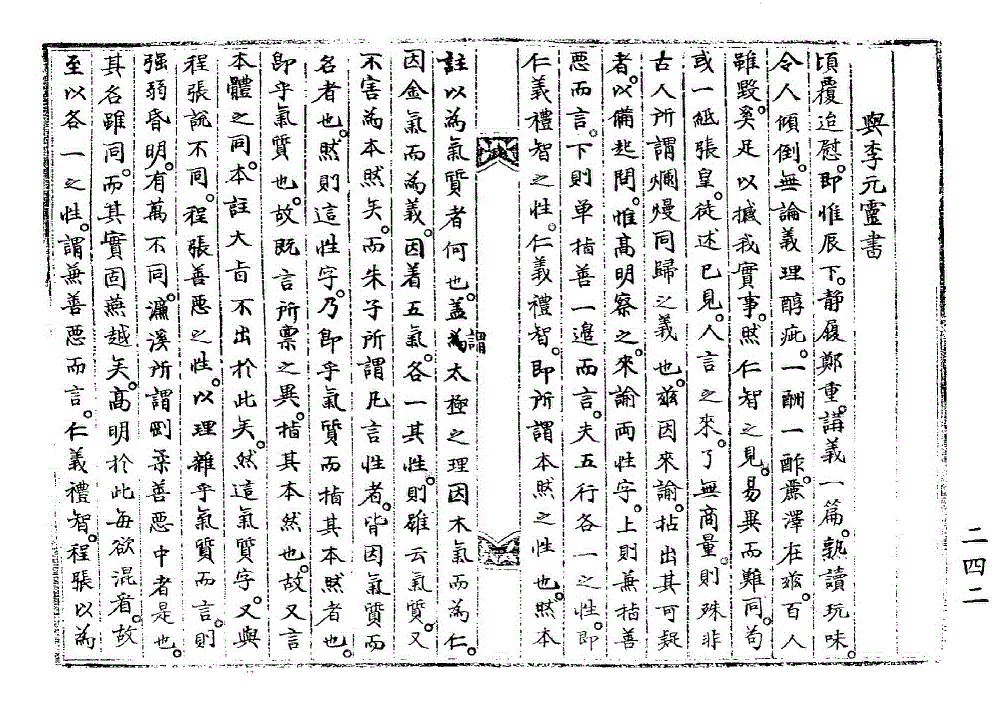 与李元灵书
与李元灵书顷覆迨慰。即惟辰下。静履郑重。讲义一篇。熟读玩味。令人倾倒。无论义理醇疵。一酬一酢。丽泽在玆。百人虽毁。奚足以撼我实事。然仁智之见。易异而难同。苟或一纸张皇。徒述己见。人言之来。了无商量。则殊非古人所谓烂熳同归之义也。玆因来谕。拈出其可疑者。以备起问。惟高明察之。来谕两性字。上则兼指善恶而言。下则单指善一边而言。夫五行各一之性。即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即所谓本然之性也。然本注以为气质者何也。盖谓太极之理因木气而为仁。因金气而为义。因着五气。各一其性。则虽云气质。又不害为本然矣。而朱子所谓凡言性者。皆因气质而名者也。然则这性字。乃即乎气质而指其本然者也。即乎气质也。故既言所禀之异。指其本然也。故又言本体之同。本注大旨不出于此矣。然这气质字。又与程张说不同。程张善恶之性。以理杂乎气质而言。则强弱昏明。有万不同。濂溪所谓刚柔善恶中者是也。其名虽同。而其实固燕越矣。高明于此每欲混看。故至以各一之性。谓兼善恶而言。仁义礼智。程张以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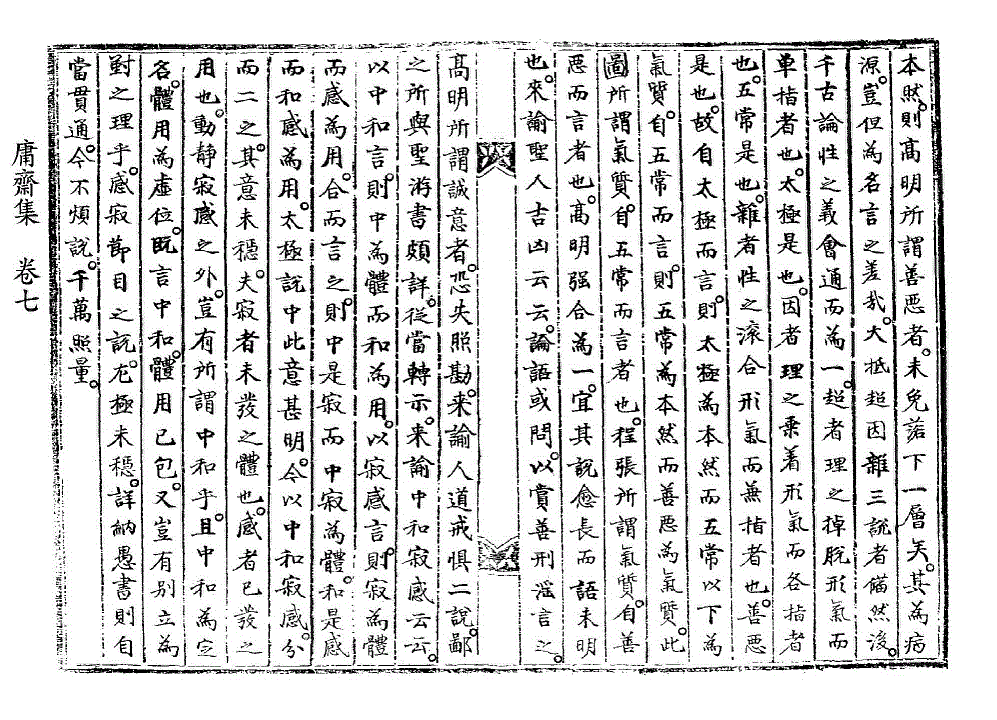 本然。则高明所谓善恶者。未免落下一层矣。其为病源。岂但为名言之差哉。大抵超因杂三说者备然后。千古论性之义会通而为一。超者理之掉脱形气而单指者也。太极是也。因者理之乘着形气而各指者也。五常是也。杂者性之滚合形气而兼指者也。善恶是也。故自太极而言。则太极为本然而五常以下为气质。自五常而言。则五常为本然而善恶为气质。此图所谓气质。自五常而言者也。程张所谓气质。自善恶而言者也。高明强合为一。宜其说愈长而语未明也。来谕圣人吉凶云云。论语或问。以赏善刑淫言之。高明所谓诚意者。恐失照勘。来谕人道戒惧二说。鄙之所与圣游书颇详。从当转示。来谕中和寂感云云。以中和言。则中为体而和为用。以寂感言。则寂为体而感为用。合而言之。则中是寂而中寂为体。和是感而和感为用。太极说中此意甚明。今以中和寂感。分而二之。其意未稳。夫寂者未发之体也。感者已发之用也。动静寂感之外。岂有所谓中和乎。且中和为定名。体用为虚位。既言中和。体用已包。又岂有别立为对之理乎。感寂节目之说。尤极未稳。详纳愚书则自当贯通。今不烦说。千万照量。
本然。则高明所谓善恶者。未免落下一层矣。其为病源。岂但为名言之差哉。大抵超因杂三说者备然后。千古论性之义会通而为一。超者理之掉脱形气而单指者也。太极是也。因者理之乘着形气而各指者也。五常是也。杂者性之滚合形气而兼指者也。善恶是也。故自太极而言。则太极为本然而五常以下为气质。自五常而言。则五常为本然而善恶为气质。此图所谓气质。自五常而言者也。程张所谓气质。自善恶而言者也。高明强合为一。宜其说愈长而语未明也。来谕圣人吉凶云云。论语或问。以赏善刑淫言之。高明所谓诚意者。恐失照勘。来谕人道戒惧二说。鄙之所与圣游书颇详。从当转示。来谕中和寂感云云。以中和言。则中为体而和为用。以寂感言。则寂为体而感为用。合而言之。则中是寂而中寂为体。和是感而和感为用。太极说中此意甚明。今以中和寂感。分而二之。其意未稳。夫寂者未发之体也。感者已发之用也。动静寂感之外。岂有所谓中和乎。且中和为定名。体用为虚位。既言中和。体用已包。又岂有别立为对之理乎。感寂节目之说。尤极未稳。详纳愚书则自当贯通。今不烦说。千万照量。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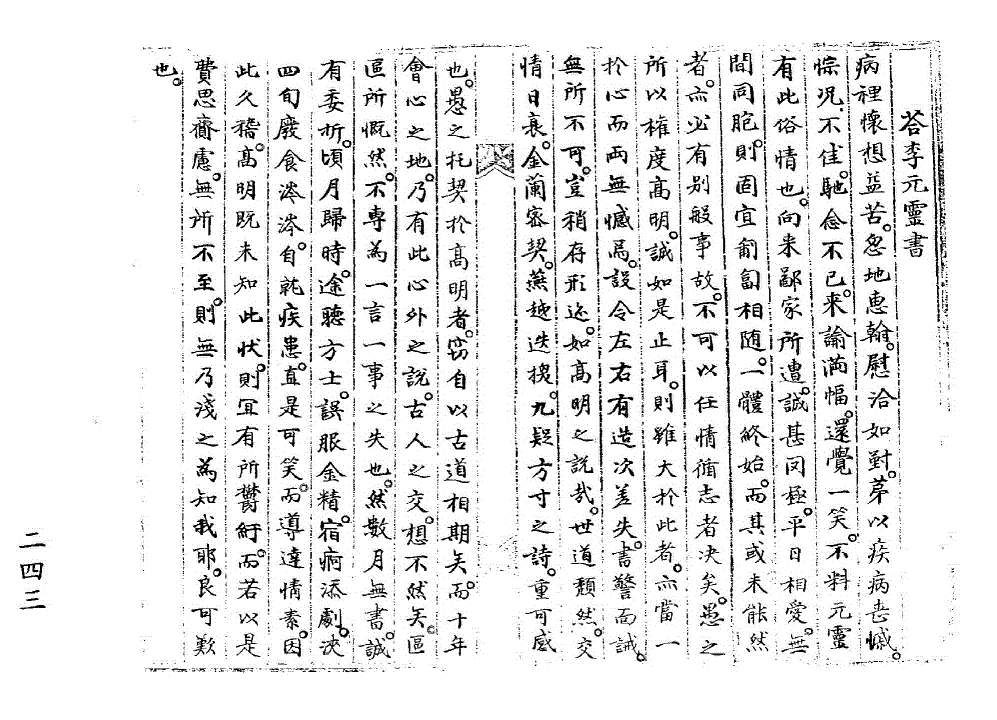 答李元灵书
答李元灵书病里怀想益苦。忽地惠翰。慰洽如对。第以疾病丧戚。悰况不佳。驰念不已。来谕满幅。还觉一笑。不料元灵有此俗情也。向来鄙家所遭。诚甚罔极。平日相爱。无间同胞。则固宜匍匐相随。一体终始。而其或未能然者。亦必有别般事故。不可以任情循志者决矣。愚之所以权度高明。诚如是止耳。则虽大于此者。亦当一于心而两无憾焉。设令左右有造次差失。书警面诫。无所不可。岂稍存形迹。如高明之说哉。世道颓然。交情日衰。金兰密契。燕越迭换。九疑方寸之诗。重可感也。愚之托契于高明者。窃自以古道相期矣。而十年会心之地。乃有此心外之说。古人之交。想不然矣。区区所慨然。不专为一言一事之失也。然数月无书。诚有委折。顷月归时。途听方士。误服金精。宿痾添剧。浃四旬废食涔涔。自就疾患。直是可笑。而导达情素。因此久稽。高明既未知此状。则宜有所郁纡。而若以是费思赍虑。无所不至。则无乃浅之为知我耶。良可叹也。
答金伯良书
岁律将暮。尊体若何。伏惟万福。顷蒙不鄙。特赐俯牍。抑扬翻覆。诲责备至。辞气之阖辟。文理之浩博。虽使南华子复生。亦莫能窥端倪。以仆之愚昧鲁劣。与闻乎此者。幸已极矣。复安敢措一辞于其间哉。然有怀不发。足下谓之不以情待。有疑不质。足下谓之不以诚交。则以愚之一得。自以为知足下不浅。而又不欲为一时之外面友。则亦安得泯然含默。无一辞于其间哉。仆天姿至愚。志操极陋。虽尝挟册读书。妄求圣贤之遗志。其于讲劘进修。实无一日用工夫。如是故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4L 页
 闻人之善而不欲与之同归。见人之过而亦不知其为非。浮沉混沦。自未免为小人之归矣。来教所谓好恶不出真心者。正中病源。顶门之针。玉钥之匙。亦未足以喻其效也。倘非平日相爱之笃。其何以及此。铭佩服膺。不容为喻。然来教缕缕。要其归趣。不过曰道义诗文之分也。讲讨酬唱之失也。愚请披露悃愊。一为足下谆复焉。噫。足下其以为诗文离乎道义乎。以为道义合乎诗文乎。以愚之所扣问者。只出于诗文乎。以愚之所奉质者。不及乎道义乎。夫道外无物。诗词文章。亦岂道外之物。是以古之有道者。其歌也为词。其言也为文。不待雕琢。浑然成章。则三百葩经。典谟春秋。即一时记述讽诵之辞。而文质得中。旨味深远。为后世师范也。则诗与文章。不可谓非道也。自是以来。王风微而斯文丧矣。寝而至于汉唐。则其所以为文者。谈文而遗实。所以为诗者。舍形而捕影。绮丽浮靡。不足为真义理之分。从此始矣。于是乎濂洛文章。一循古法。刊落浮华。浑浩朴雅。馀味无穷。盖其所存主者。具原于性命形气之实。而不淫乎风花雪月之间。则其发之声气者。自不得不尔矣。典谟春秋三百篇馀音。焕然复明于斯矣。后之学者。若以三代为
闻人之善而不欲与之同归。见人之过而亦不知其为非。浮沉混沦。自未免为小人之归矣。来教所谓好恶不出真心者。正中病源。顶门之针。玉钥之匙。亦未足以喻其效也。倘非平日相爱之笃。其何以及此。铭佩服膺。不容为喻。然来教缕缕。要其归趣。不过曰道义诗文之分也。讲讨酬唱之失也。愚请披露悃愊。一为足下谆复焉。噫。足下其以为诗文离乎道义乎。以为道义合乎诗文乎。以愚之所扣问者。只出于诗文乎。以愚之所奉质者。不及乎道义乎。夫道外无物。诗词文章。亦岂道外之物。是以古之有道者。其歌也为词。其言也为文。不待雕琢。浑然成章。则三百葩经。典谟春秋。即一时记述讽诵之辞。而文质得中。旨味深远。为后世师范也。则诗与文章。不可谓非道也。自是以来。王风微而斯文丧矣。寝而至于汉唐。则其所以为文者。谈文而遗实。所以为诗者。舍形而捕影。绮丽浮靡。不足为真义理之分。从此始矣。于是乎濂洛文章。一循古法。刊落浮华。浑浩朴雅。馀味无穷。盖其所存主者。具原于性命形气之实。而不淫乎风花雪月之间。则其发之声气者。自不得不尔矣。典谟春秋三百篇馀音。焕然复明于斯矣。后之学者。若以三代为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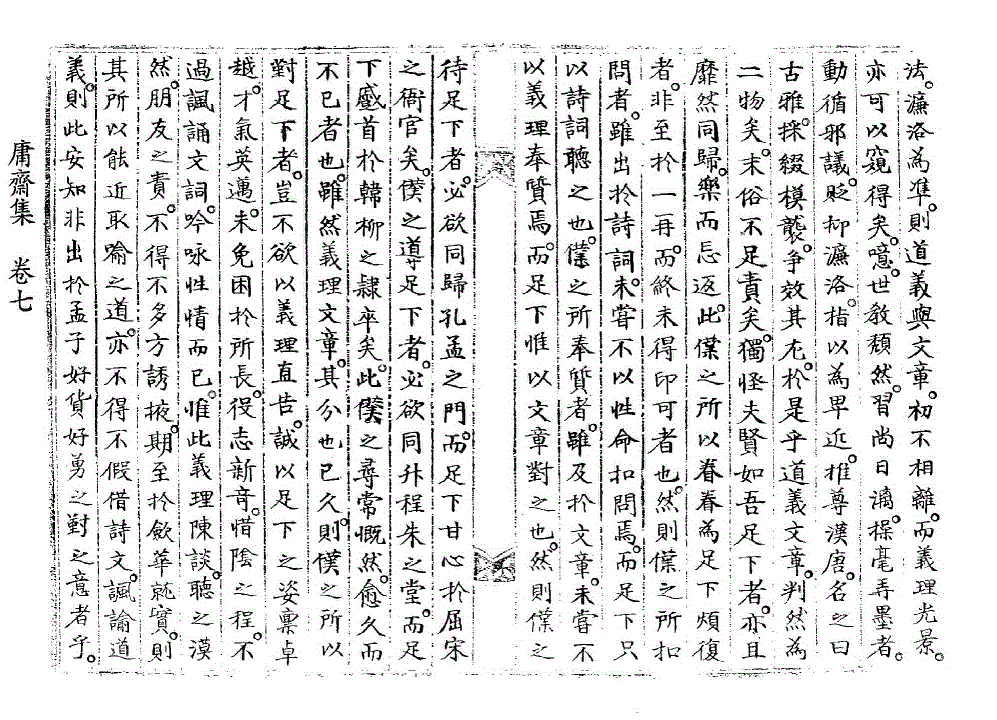 法。濂洛为准。则道义与文章。初不相离。而义理光景。亦可以窥得矣。噫。世教颓然。习尚日漓。操毫弄墨者。动循邪议。贬抑濂洛。指以为卑近。推尊汉唐。名之曰古雅。采缀模袭。争效其尤。于是乎道义文章。判然为二物矣。末俗不足责矣。独怪夫贤如吾足下者。亦且靡然同归。乐而忘返。此仆之所以眷眷为足下烦复者。非至于一再。而终未得印可者也。然则仆之所扣问者。虽出于诗词。未尝不以性命扣问焉。而足下只以诗词听之也。仆之所奉质者。虽及于文章。未尝不以义理奉质焉。而足下惟以文章对之也。然则仆之待足下者。必欲同归孔孟之门。而足下甘心于屈宋之衙官矣。仆之导足下者。必欲同升程朱之堂。而足下蹙首于韩柳之隶卒矣。此仆之寻常慨然。愈久而不已者也。虽然义理文章。其分也已久。则仆之所以对足下者。岂不欲以义理直告。诚以足下之姿禀卓越。才气英迈。未免困于所长。役志新奇。惜阴之程。不过讽诵文词。吟咏性情而已。惟此义理陈谈。听之漠然。朋友之责。不得不多方诱掖。期至于敛华就实。则其所以能近取喻之道。亦不得不假借诗文。讽谕道义。则此安知非出于孟子好货好勇之对之意者乎。
法。濂洛为准。则道义与文章。初不相离。而义理光景。亦可以窥得矣。噫。世教颓然。习尚日漓。操毫弄墨者。动循邪议。贬抑濂洛。指以为卑近。推尊汉唐。名之曰古雅。采缀模袭。争效其尤。于是乎道义文章。判然为二物矣。末俗不足责矣。独怪夫贤如吾足下者。亦且靡然同归。乐而忘返。此仆之所以眷眷为足下烦复者。非至于一再。而终未得印可者也。然则仆之所扣问者。虽出于诗词。未尝不以性命扣问焉。而足下只以诗词听之也。仆之所奉质者。虽及于文章。未尝不以义理奉质焉。而足下惟以文章对之也。然则仆之待足下者。必欲同归孔孟之门。而足下甘心于屈宋之衙官矣。仆之导足下者。必欲同升程朱之堂。而足下蹙首于韩柳之隶卒矣。此仆之寻常慨然。愈久而不已者也。虽然义理文章。其分也已久。则仆之所以对足下者。岂不欲以义理直告。诚以足下之姿禀卓越。才气英迈。未免困于所长。役志新奇。惜阴之程。不过讽诵文词。吟咏性情而已。惟此义理陈谈。听之漠然。朋友之责。不得不多方诱掖。期至于敛华就实。则其所以能近取喻之道。亦不得不假借诗文。讽谕道义。则此安知非出于孟子好货好勇之对之意者乎。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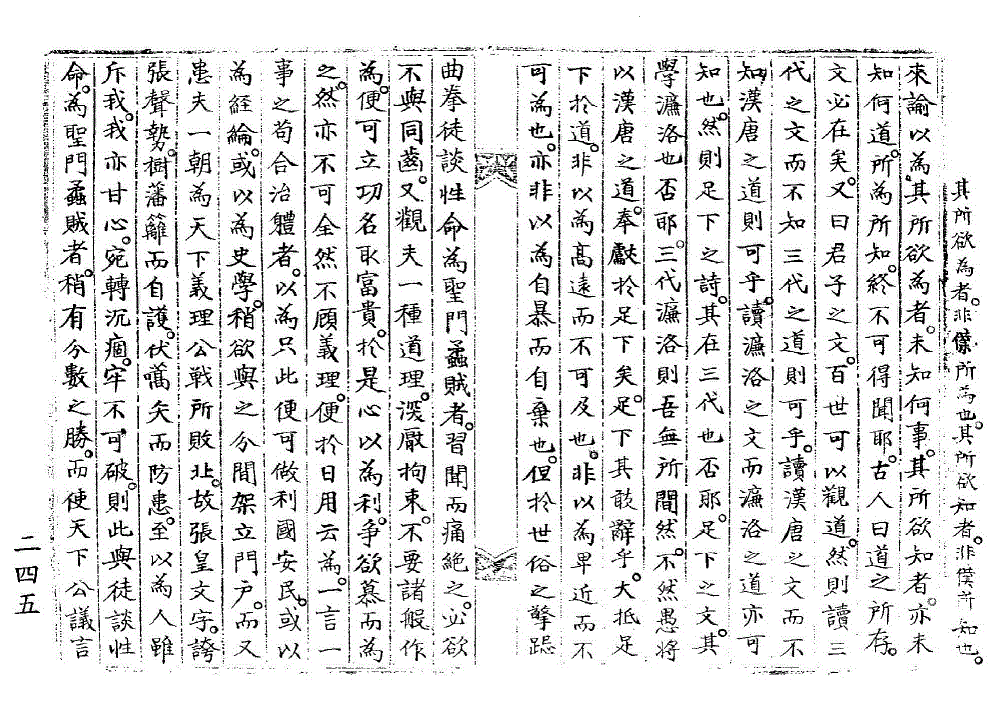 来谕以为其所欲为者。非仆所为也。其所欲知者。非仆所知也。其所欲为者。未知何事。其所欲知者。亦未知何道。所为所知。终不可得闻耶。古人曰道之所存。文必在矣。又曰君子之文。百世可以观道。然则读三代之文而不知三代之道则可乎。读汉唐之文而不知汉唐之道则可乎。读濂洛之文而濂洛之道亦可知也。然则足下之诗。其在三代也否耶。足下之文。其学濂洛也否耶。三代濂洛则吾无所间然。不然愚将以汉唐之道。奉献于足下矣。足下其敢辞乎。大抵足下于道。非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也。非以为卑近而不可为也。亦非以为自暴而自弃也。但于世俗之擎跽曲拳徒谈性命为圣门蟊贼者。习闻而痛绝之。必欲不与同齿。又观夫一种道理。深厌拘束。不要诸般作为。便可立功名取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亦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便于日用云为。一言一事之苟合治体者。以为只此便可做利国安民。或以为经纶。或以为史学。稍欲与之分间架立门户。而又患夫一朝为天下义理公战所败北。故张皇文字。誇张声势。树藩篱而自护。伏嚆矢而防患。至以为人虽斥我。我亦甘心。宛转沉痼。牢不可破。则此与徒谈性命。为圣门蟊贼者。稍有分数之胜。而使天下公议言
来谕以为其所欲为者。非仆所为也。其所欲知者。非仆所知也。其所欲为者。未知何事。其所欲知者。亦未知何道。所为所知。终不可得闻耶。古人曰道之所存。文必在矣。又曰君子之文。百世可以观道。然则读三代之文而不知三代之道则可乎。读汉唐之文而不知汉唐之道则可乎。读濂洛之文而濂洛之道亦可知也。然则足下之诗。其在三代也否耶。足下之文。其学濂洛也否耶。三代濂洛则吾无所间然。不然愚将以汉唐之道。奉献于足下矣。足下其敢辞乎。大抵足下于道。非以为高远而不可及也。非以为卑近而不可为也。亦非以为自暴而自弃也。但于世俗之擎跽曲拳徒谈性命为圣门蟊贼者。习闻而痛绝之。必欲不与同齿。又观夫一种道理。深厌拘束。不要诸般作为。便可立功名取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亦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便于日用云为。一言一事之苟合治体者。以为只此便可做利国安民。或以为经纶。或以为史学。稍欲与之分间架立门户。而又患夫一朝为天下义理公战所败北。故张皇文字。誇张声势。树藩篱而自护。伏嚆矢而防患。至以为人虽斥我。我亦甘心。宛转沉痼。牢不可破。则此与徒谈性命。为圣门蟊贼者。稍有分数之胜。而使天下公议言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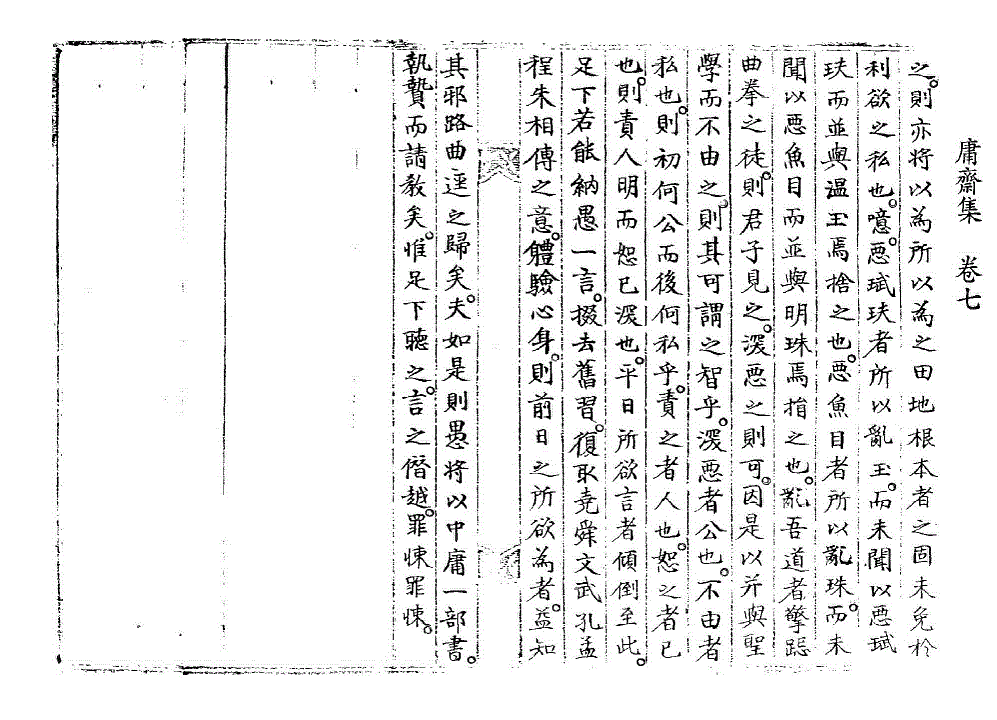 之。则亦将以为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之固未免于利欲之私也。噫。恶珷玞者所以乱玉。而未闻以恶珷玞而并与温玉焉舍之也。恶鱼目者所以乱珠。而未闻以恶鱼目而并与明珠焉捐之也。乱吾道者擎跽曲拳之徒。则君子见之。深恶之则可。因是以并与圣学而不由之。则其可谓之智乎。深恶者公也。不由者私也。则初何公而后何私乎。责之者人也。恕之者己也。则责人明而恕己深也。平日所欲言者倾倒至此。足下若能纳愚一言。掇去旧习。复取尧舜文武孔孟程朱相传之意。体验心身。则前日之所欲为者。益知其邪路曲径之归矣。夫如是则愚将以中庸一部书。执贽而请教矣。惟足下听之。言之僭越。罪悚罪悚。
之。则亦将以为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之固未免于利欲之私也。噫。恶珷玞者所以乱玉。而未闻以恶珷玞而并与温玉焉舍之也。恶鱼目者所以乱珠。而未闻以恶鱼目而并与明珠焉捐之也。乱吾道者擎跽曲拳之徒。则君子见之。深恶之则可。因是以并与圣学而不由之。则其可谓之智乎。深恶者公也。不由者私也。则初何公而后何私乎。责之者人也。恕之者己也。则责人明而恕己深也。平日所欲言者倾倒至此。足下若能纳愚一言。掇去旧习。复取尧舜文武孔孟程朱相传之意。体验心身。则前日之所欲为者。益知其邪路曲径之归矣。夫如是则愚将以中庸一部书。执贽而请教矣。惟足下听之。言之僭越。罪悚罪悚。答李伯讷(敏辅)书
理一说。可感勤示。而起郁则有之。大抵理气一而二,二而一两句备然后。理气不落一偏。五常说。二而一之论也。气质说。一而二之论也。若如高论。则先儒两句语。亦将刊去上句。岂理也哉。高明才锐识超。观理甚易。往往不劳而得。是则可仰。而第不免困于聪明。有时入于偏枯之科。惜哉。义理无穷。岂一蹴可到。无某工夫。看某不得。非晦翁语乎。先辈苦心积工。正宜玩索而得。恐难草草觑破。冷语了断。幸更详答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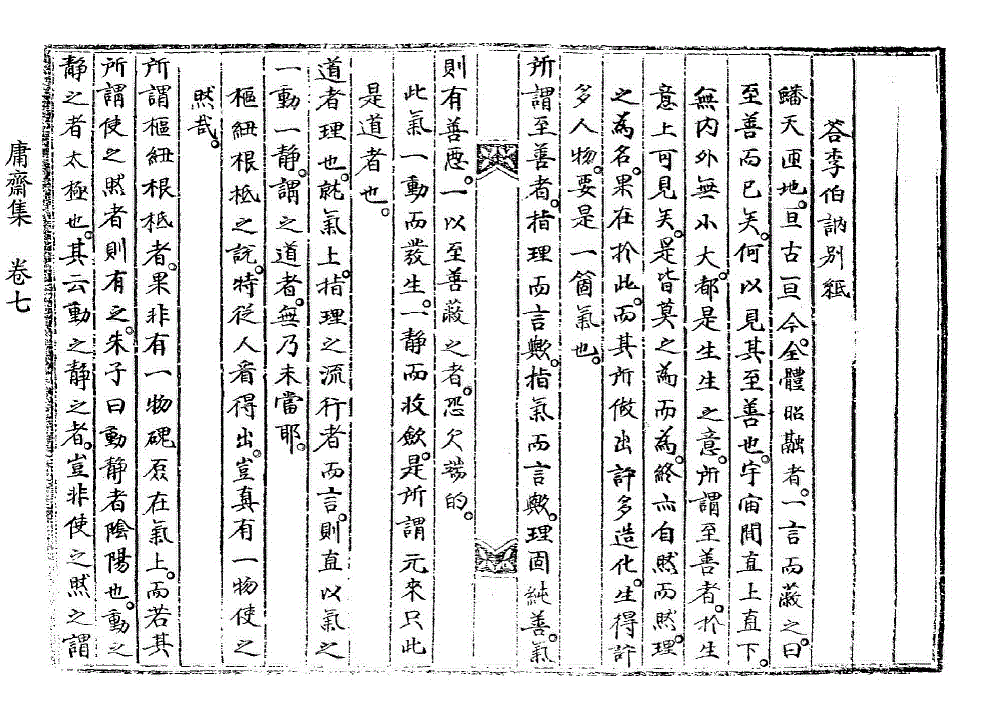 答李伯讷别纸
答李伯讷别纸蟠天匝地。亘古亘今。全体昭融者。一言而蔽之。曰至善而已矣。何以见其至善也。宇宙间直上直下。无内外无小大。都是生生之意。所谓至善者。于生意上可见矣。是皆莫之为而为。终亦自然而然。理之为名。果在于此。而其所做出许多造化。生得许多人物。要是一个气也。
所谓至善者。指理而言欤。指气而言欤。理固纯善。气则有善恶。一以至善蔽之者。恐欠端的。
此气一动而发生。一静而收敛。是所谓元来只此是道者也。
道者理也。就气上。指理之流行者而言。则直以气之一动一静。谓之道者。无乃未当耶。
枢纽根柢之说。特从人看得出。岂真有一物使之然哉。
所谓枢纽根柢者。果非有一物磈磊在气上。而若其所谓使之然者则有之。朱子曰动静者阴阳也。动之静之者太极也。其云动之静之者。岂非使之然之谓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7L 页
 欤。
欤。是故朱子之训天。直以理断之者。亦即气而言。程子以形体谓之天。以性情谓之乾。以主宰谓之帝。只就一个地头。截得上下最分明。帝是天之自然处。乾是天之当然处。何有空隙。可安排理字者乎。
天字有以理言者。天且不违是也。有以气言者。天何言哉是也。此则有偏言专言之别。而本非以理气无间而言也。理与气一而二二而一言。理言气。都在一处。果无彼此可指空隙可排。而若云全无主宰全无分别。则又非一而二之义也。
人皆谓理本至善。而不知其气之至善。徒见气之末流之恶。而不知其本体之湛一。苟非气之湛一。何由而见其理之善乎。
气之本体固澹一。而以全体言之。清浊刚柔亦在其中。若云全体纯善。则所谓末流之恶。亦从何处生出耶。且气之澹一处。理体固呈露。而理体之纯善。本自纯善。初不待气而善也。
今人论理。大抵承袭依㨾。论人物禀受。则掉了形气。泛说公共道理。其于性之名义。不恤其不着。
论人物性名义甚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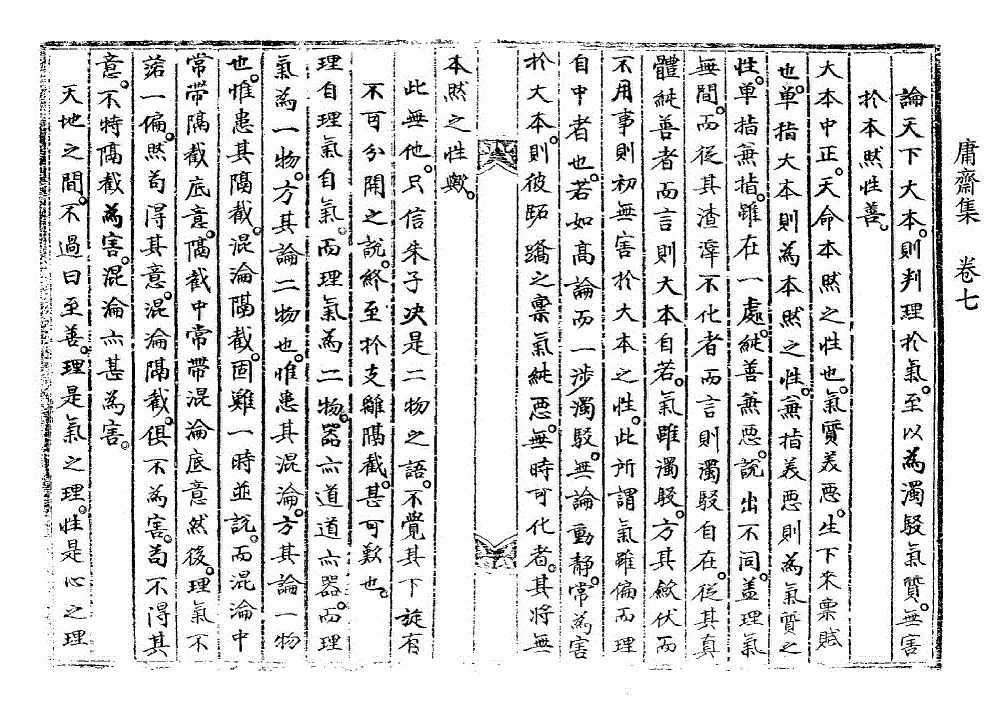 论天下大本。则判理于气。至以为浊驳气质。无害于本然性善。
论天下大本。则判理于气。至以为浊驳气质。无害于本然性善。大本中正。天命本然之性也。气质美恶。生下来禀赋也。单指大本则为本然之性。兼指美恶则为气质之性。单指兼指。虽在一处。纯善兼恶。说出不同。盖理气无间。而从其渣滓不化者而言则浊驳自在。从其真体纯善者而言则大本自若。气虽浊驳。方其敛伏而不用事则初无害于大本之性。此所谓气虽偏而理自中者也。若如高论而一涉浊驳。无论动静。常为害于大本。则彼蹠蹻之禀气纯恶。无时可化者。其将无本然之性欤。
此无他。只信朱子决是二物之语。不觉其下旋有不可分开之说。终至于支离隔截。甚可叹也。
理自理气自气。而理气为二物。器亦道道亦器。而理气为一物。方其论二物也。惟患其混沦。方其论一物也。惟患其隔截。混沦隔截。固难一时并说。而混沦中常带隔截底意。隔截中常带混沦底意然后。理气不落一偏。然苟得其意。混沦隔截。俱不为害。苟不得其意。不特隔截为害。混沦亦甚为害。
天地之间。不过曰至善。理是气之理。性是心之理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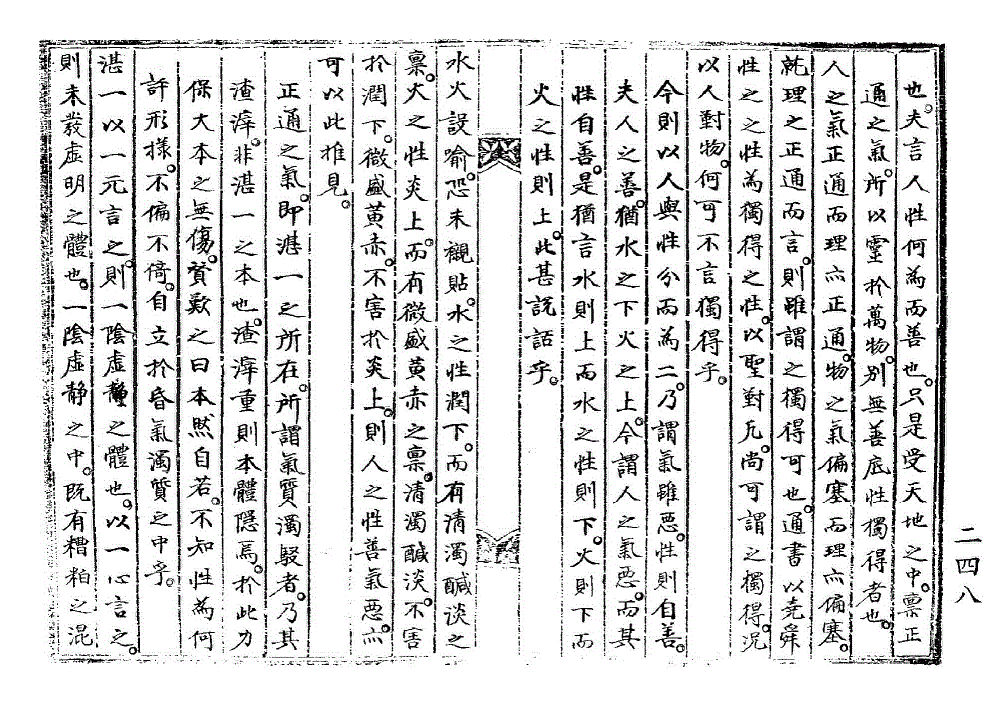 也。夫言人性何为而善也。只是受天地之中。禀正通之气。所以灵于万物。别无善底性独得者也。
也。夫言人性何为而善也。只是受天地之中。禀正通之气。所以灵于万物。别无善底性独得者也。人之气正通而理亦正通。物之气偏塞而理亦偏塞。就理之正通而言。则虽谓之独得可也。通书以尧舜性之之性为独得之性。以圣对凡。尚可谓之独得。况以人对物。何可不言独得乎。
今则以人与性分而为二。乃谓气虽恶。性则自善。夫人之善。犹水之下火之上。今谓人之气恶。而其性自善。是犹言水则上而水之性则下。火则下而火之性则上。此甚说话乎。
水火设喻。恐未衬贴。水之性润下。而有清浊咸淡之禀。火之性炎上。而有微盛黄赤之禀。清浊咸淡。不害于润下。微盛黄赤。不害于炎上。则人之性善气恶。亦可以此推见。
正通之气。即湛一之所在。所谓气质浊驳者。乃其渣滓。非湛一之本也。渣滓重则本体隐焉。于此力保大本之无伤。赞叹之曰本然自若。不知性为何许形㨾。不偏不倚。自立于昏气浊质之中乎。
湛一以一元言之。则一阴虚静之体也。以一心言之。则未发虚明之体也。一阴虚静之中。既有糟粕之混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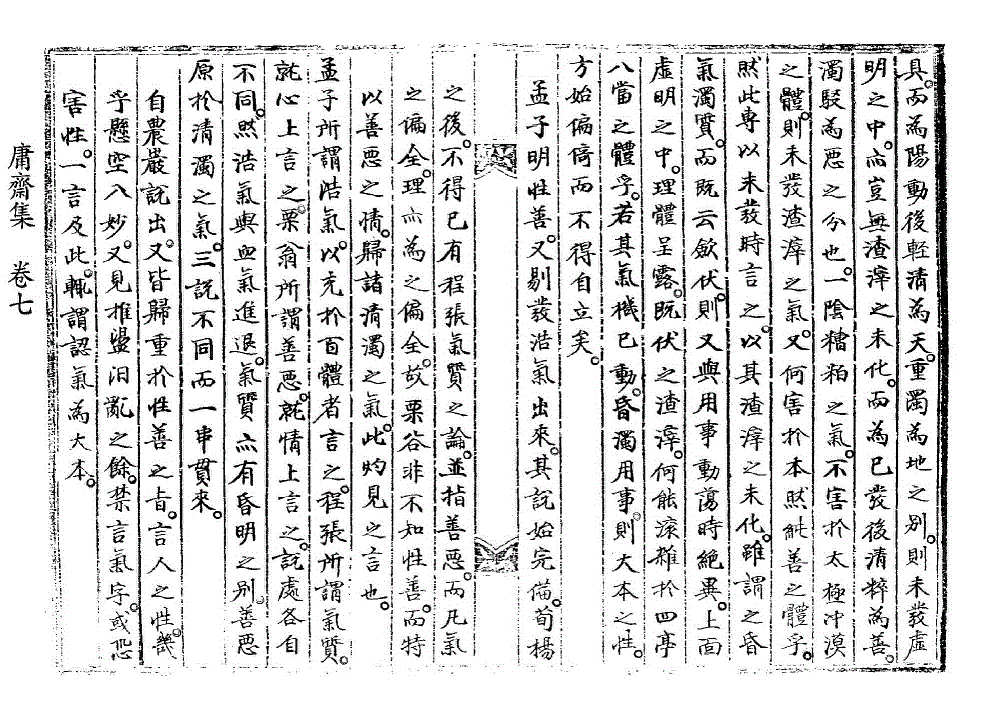 具。而为阳动后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之别。则未发虚明之中。亦岂无渣滓之未化。而为已发后清粹为善。浊驳为恶之分也。一阴糟粕之气。不害于太极冲漠之体。则未发渣滓之气。又何害于本然纯善之体乎。然此专以未发时言之。以其渣滓之未化。虽谓之昏气浊质。而既云敛伏。则又与用事动荡时绝异。上面虚明之中。理体呈露。既伏之渣滓。何能滚杂于四亭八当之体乎。若其气机已动。昏浊用事。则大本之性。方始偏倚而不得自立矣。
具。而为阳动后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之别。则未发虚明之中。亦岂无渣滓之未化。而为已发后清粹为善。浊驳为恶之分也。一阴糟粕之气。不害于太极冲漠之体。则未发渣滓之气。又何害于本然纯善之体乎。然此专以未发时言之。以其渣滓之未化。虽谓之昏气浊质。而既云敛伏。则又与用事动荡时绝异。上面虚明之中。理体呈露。既伏之渣滓。何能滚杂于四亭八当之体乎。若其气机已动。昏浊用事。则大本之性。方始偏倚而不得自立矣。孟子明性善。又剔发浩气出来。其说始完备。荀杨之后。不得已有程张气质之论。并指善恶。而凡气之偏全。理亦为之偏全。故栗谷非不知性善。而特以善恶之情。归诸清浊之气。此灼见之言也。
孟子所谓浩气。以充于百体者言之。程张所谓气质。就心上言之。栗翁所谓善恶。就情上言之。说处各自不同。然浩气与血气进退。气质亦有昏明之别。善恶原于清浊之气。三说不同而一串贯来。
自农岩说出。又皆归重于性善之旨。言人之性。几乎悬空入妙。又见推荡汩乱之馀。禁言气字。或恐害性。一言及此。辄谓认气为大本。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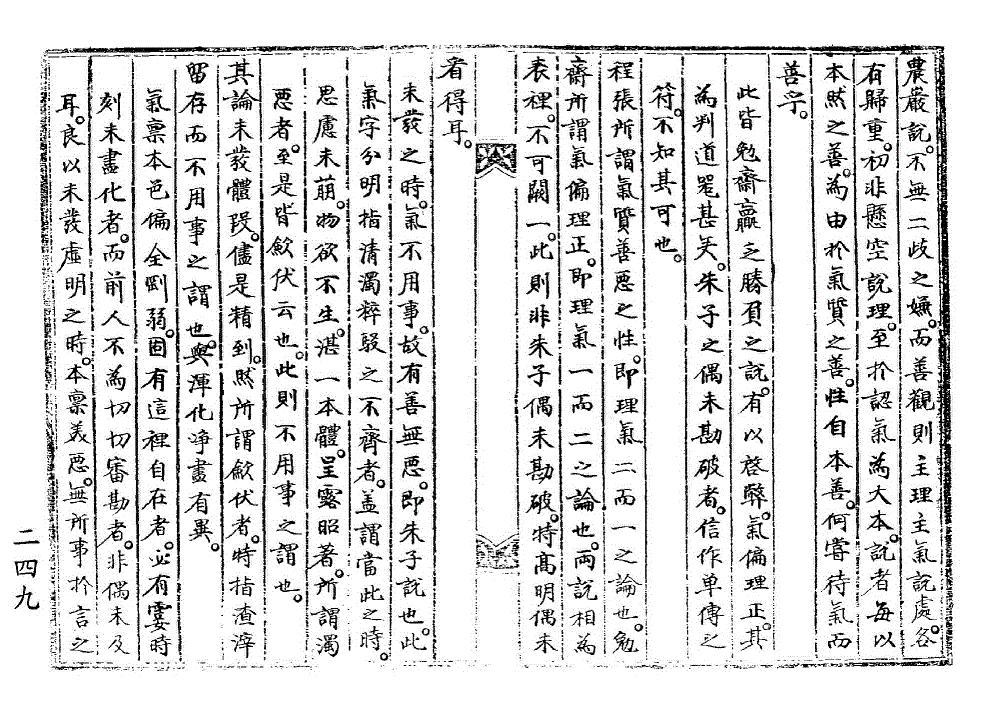 农岩说。不无二歧之嫌。而善观则主理主气说处。各有归重。初非悬空说理。至于认气为大本。说者每以本然之善。为由于气质之善。性自本善。何尝待气而善乎。
农岩说。不无二歧之嫌。而善观则主理主气说处。各有归重。初非悬空说理。至于认气为大本。说者每以本然之善。为由于气质之善。性自本善。何尝待气而善乎。此皆勉斋赢乏胜负之说。有以启弊。气偏理正。其为判道器甚矣。朱子之偶未勘破者。信作单传之符。不知其可也。
程张所谓气质善恶之性。即理气二而一之论也。勉斋所谓气偏理正。即理气一而二之论也。两说相为表里。不可阙一。此则非朱子偶未勘破。特高明偶未看得耳。
未发之时。气不用事。故有善无恶。即朱子说也。此气字分明指清浊粹驳之不齐者。盖谓当此之时。思虑未萌。物欲不生。湛一本体。呈露昭著。所谓浊恶者。至是皆敛伏云也。此则不用事之谓也。
其论未发体段。尽是精到。然所谓敛伏者。特指渣滓留存而不用事之谓也。与浑化净尽有异。
气禀本色偏全刚弱。固有这里自在者。必有霎时刻未尽化者。而前人不为切切审勘者。非偶未及耳。良以未发虚明之时。本禀美恶。无所事于言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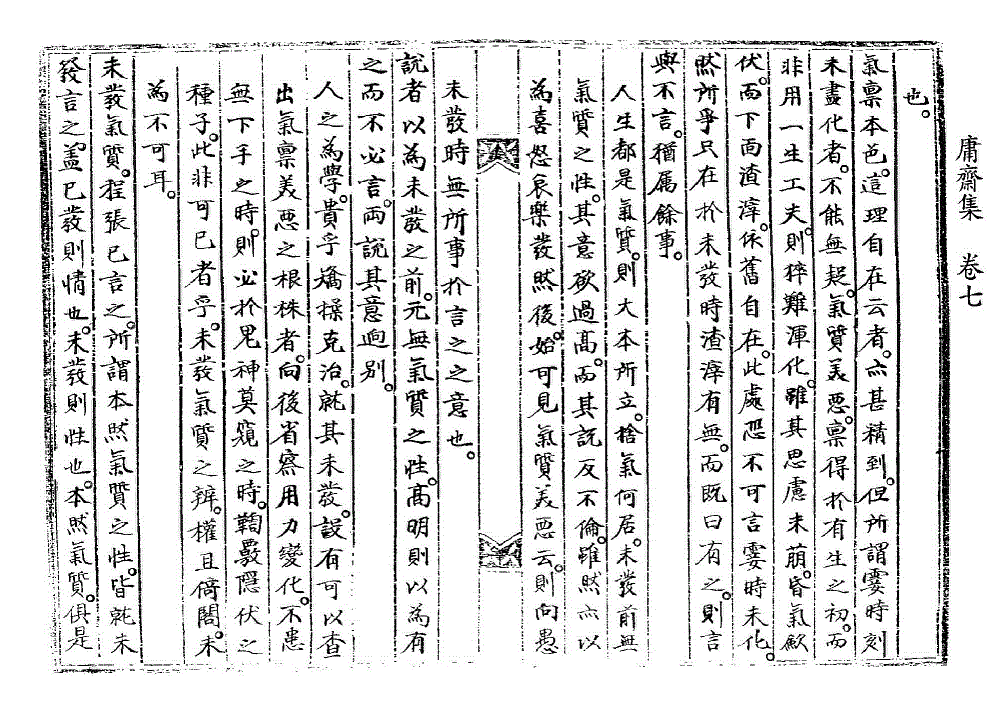 也。
也。气禀本色。这理自在云者。亦甚精到。但所谓霎时刻未尽化者。不能无疑。气质美恶。禀得于有生之初。而非用一生工夫。则猝难浑化。虽其思虑未萌。昏气敛伏。而下面渣滓。依旧自在。此处恐不可言霎时未化。然所争只在于未发时渣滓有无。而既曰有之。则言与不言。犹属馀事。
人生都是气质。则大本所立。舍气何居。未发前无气质之性。其意欲过高。而其说反不伦。虽然亦以为喜怒哀乐发然后。始可见气质美恶云。则向愚未发时无所事于言之之意也。
说者以为未发之前。元无气质之性。高明则以为有之而不必言。两说其意迥别。
人之为学。贵乎矫揉克治。就其未发。设有可以查出气禀美恶之根株者。向后省察用力变化。不患无下手之时。则必于鬼神莫窥之时。鞫覈隐伏之种子。此非可已者乎。未发气质之辨。权且倚阁。未为不可耳。
未发气质。程张已言之。所谓本然气质之性。皆就未发言之。盖已发则情也。未发则性也。本然气质。俱是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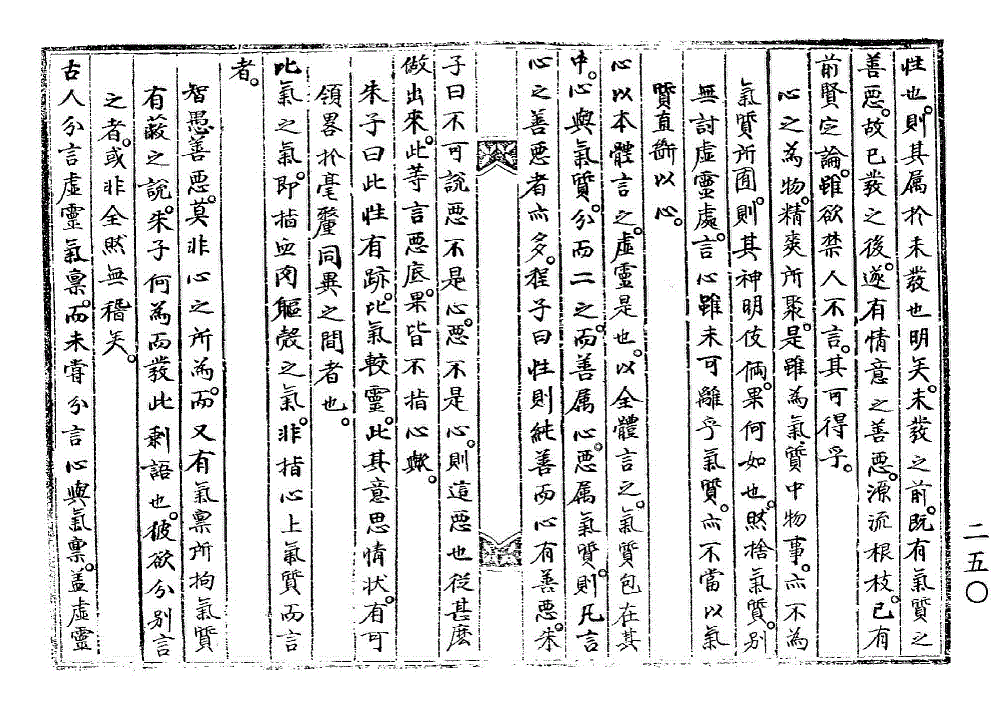 性也。则其属于未发也明矣。未发之前。既有气质之善恶。故已发之后。遂有情意之善恶。源流根枝。已有前贤定论。虽欲禁人不言。其可得乎。
性也。则其属于未发也明矣。未发之前。既有气质之善恶。故已发之后。遂有情意之善恶。源流根枝。已有前贤定论。虽欲禁人不言。其可得乎。心之为物。精爽所聚。是虽为气质中物事。亦不为气质所囿。则其神明伎俩。果何如也。然舍气质。别无讨虚灵处。言心虽未可离乎气质。亦不当以气质直断以心。
心以本体言之。虚灵是也。以全体言之。气质包在其中。心与气质。分而二之。而善属心。恶属气质。则凡言心之善恶者亦多。程子曰性则纯善而心有善恶。朱子曰不可说恶不是心。恶不是心。则这恶也从甚么做出来。此等言恶底。果皆不指心欤。
朱子曰此性有迹。比气较灵。此其意思情状。有可领略于毫釐同异之间者也。
比气之气。即指血肉躯壳之气。非指心上气质而言者。
智愚善恶。莫非心之所为。而又有气禀所拘气质有蔽之说。朱子何为而发此剩语也。彼欲分别言之者。或非全然无稽矣。
古人分言虚灵气禀。而未尝分言心与气禀。盖虚灵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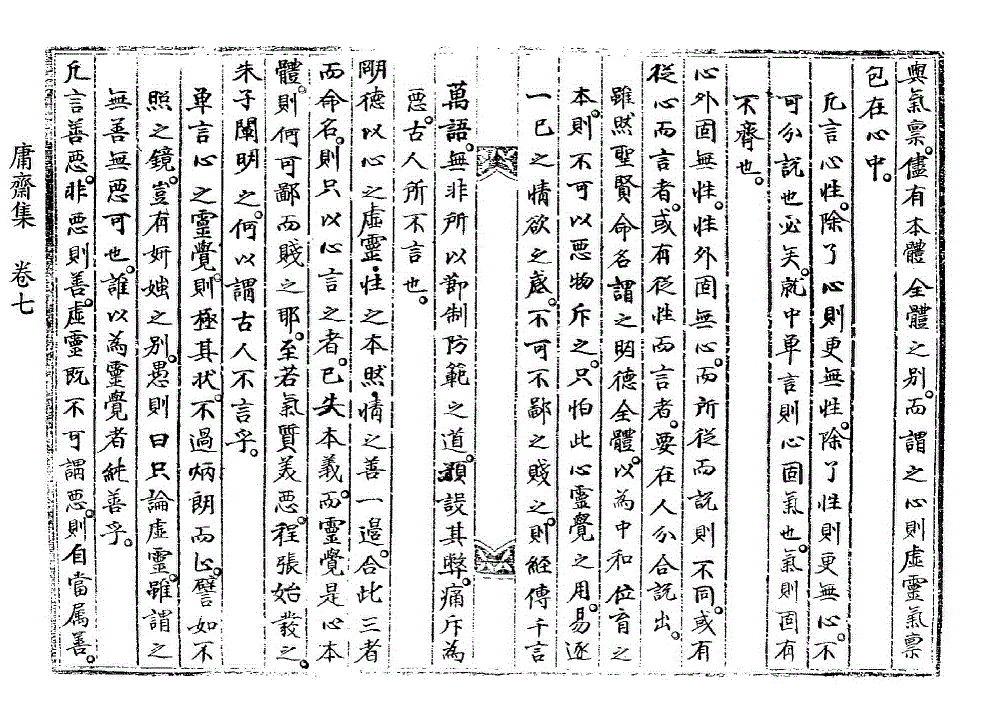 与气禀。尽有本体全体之别。而谓之心则虚灵气禀包在心中。
与气禀。尽有本体全体之别。而谓之心则虚灵气禀包在心中。凡言心性。除了心则更无性。除了性则更无心。不可分说也必矣。就中单言则心固气也。气则固有不齐也。
心外固无性。性外固无心。而所从而说则不同。或有从心而言者。或有从性而言者。要在人分合说出。
虽然圣贤命名谓之明德全体。以为中和位育之本。则不可以恶物斥之。只怕此心灵觉之用。易逐一己之情欲之感。不可不鄙之贱之。则经传千言万语。无非所以节制防范之道。预设其弊。痛斥为恶。古人所不言也。
明德以心之虚灵,性之本然,情之善一边。合此三者而命名。则只以心言之者。已失本义。而灵觉是心本体。则何可鄙而贱之耶。至若气质美恶。程张始发之。朱子阐明之。何以谓古人不言乎。
单言心之灵觉。则极其状。不过炳朗而止。譬如不照之镜。岂有妍媸之别。愚则曰只论虚灵。虽谓之无善无恶可也。谁以为灵觉者纯善乎。
凡言善恶。非恶则善。虚灵既不可谓恶。则自当属善。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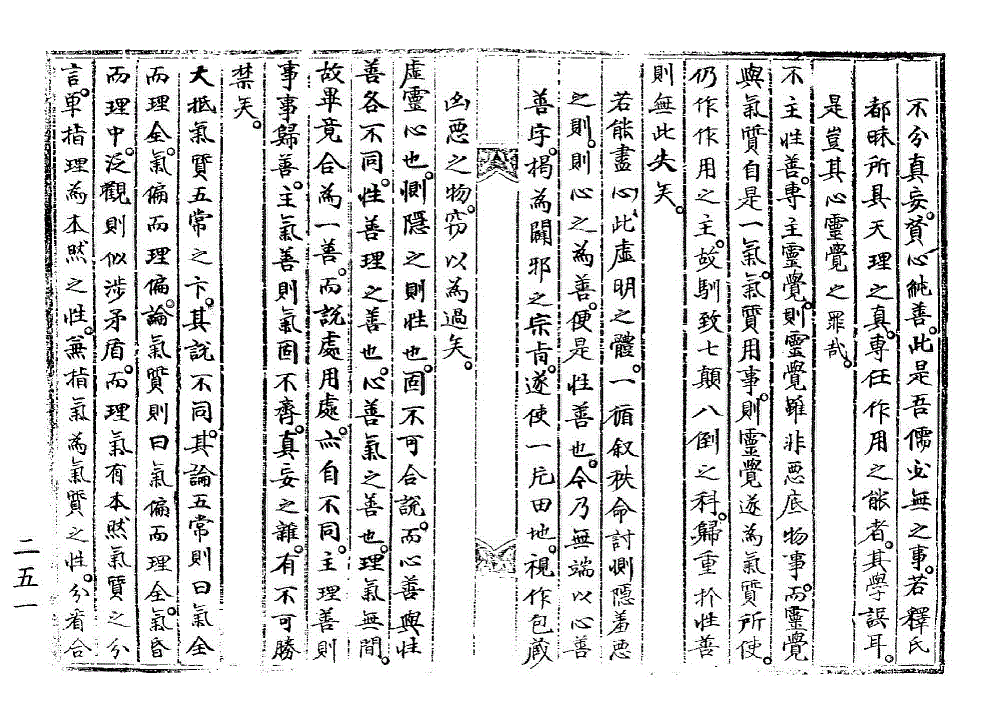 不分真妄。赞心纯善。此是吾儒必无之事。若释氏都昧所具天理之真。专任作用之能者。其学误耳。是岂其心灵觉之罪哉。
不分真妄。赞心纯善。此是吾儒必无之事。若释氏都昧所具天理之真。专任作用之能者。其学误耳。是岂其心灵觉之罪哉。不主性善。专主灵觉。则灵觉虽非恶底物事。而灵觉与气质自是一气。气质用事。则灵觉遂为气质所使。仍作作用之主。故驯致七颠八倒之科。归重于性善则无此失矣。
若能尽此心虚明之体。一循叙秩命讨恻隐羞恶之则。则心之为善。便是性善也。今乃无端以心善善字。揭为辟邪之宗旨。遂使一片田地。视作包藏凶恶之物。窃以为过矣。
虚灵心也。恻隐之则性也。固不可合说。而心善与性善各不同。性善理之善也。心善气之善也。理气无间。故毕竟合为一善。而说处用处。亦自不同。主理善则事事归善。主气善则气固不齐。真妄之杂。有不可胜禁矣。
大抵气质五常之卞。其说不同。其论五常则曰气全而理全。气偏而理偏。论气质则曰气偏而理全。气昏而理中。泛观则似涉矛盾。而理气有本然气质之分言。单指理为本然之性。兼指气为气质之性。分看合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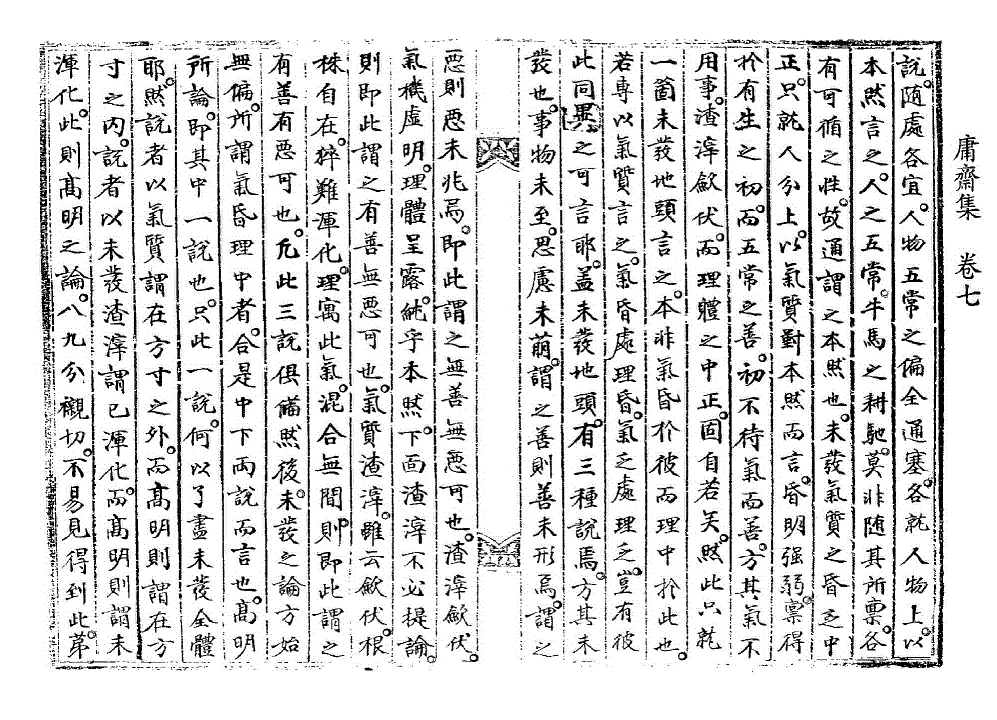 说。随处各宜。人物五常之偏全通塞。各就人物上。以本然言之。人之五常。牛马之耕驰。莫非随其所禀。各有可循之性。故通谓之本然也。未发气质之昏乏中正。只就人分上。以气质对本然而言。昏明强弱。禀得于有生之初。而五常之善。初不待气而善。方其气不用事。渣滓敛伏。而理体之中正。固自若矣。然此只就一个未发地头言之。本非气昏于彼而理中于此也。若专以气质言之。气昏处理昏。气乏处理乏。岂有彼此同异之可言耶。盖未发地头。有三种说焉。方其未发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谓之善则善未形焉。谓之恶则恶未兆焉。即此谓之无善无恶可也。渣滓敛伏。气机虚明。理体呈露。纯乎本然。下面渣滓不必提论。则即此谓之有善无恶可也。气质渣滓。虽云敛伏。根株自在。猝难浑化。理寓此气。混合无间。则即此谓之有善有恶可也。凡此三说俱备然后。未发之论方始无偏。所谓气昏理中者。合是中下两说而言也。高明所论。即其中一说也。只此一说。何以了尽未发全体耶。然说者以气质谓在方寸之外。而高明则谓在方寸之内。说者以未发渣滓谓已浑化。而高明则谓未浑化。此则高明之论。八九分衬切。不易见得到此。第
说。随处各宜。人物五常之偏全通塞。各就人物上。以本然言之。人之五常。牛马之耕驰。莫非随其所禀。各有可循之性。故通谓之本然也。未发气质之昏乏中正。只就人分上。以气质对本然而言。昏明强弱。禀得于有生之初。而五常之善。初不待气而善。方其气不用事。渣滓敛伏。而理体之中正。固自若矣。然此只就一个未发地头言之。本非气昏于彼而理中于此也。若专以气质言之。气昏处理昏。气乏处理乏。岂有彼此同异之可言耶。盖未发地头。有三种说焉。方其未发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谓之善则善未形焉。谓之恶则恶未兆焉。即此谓之无善无恶可也。渣滓敛伏。气机虚明。理体呈露。纯乎本然。下面渣滓不必提论。则即此谓之有善无恶可也。气质渣滓。虽云敛伏。根株自在。猝难浑化。理寓此气。混合无间。则即此谓之有善有恶可也。凡此三说俱备然后。未发之论方始无偏。所谓气昏理中者。合是中下两说而言也。高明所论。即其中一说也。只此一说。何以了尽未发全体耶。然说者以气质谓在方寸之外。而高明则谓在方寸之内。说者以未发渣滓谓已浑化。而高明则谓未浑化。此则高明之论。八九分衬切。不易见得到此。第庸斋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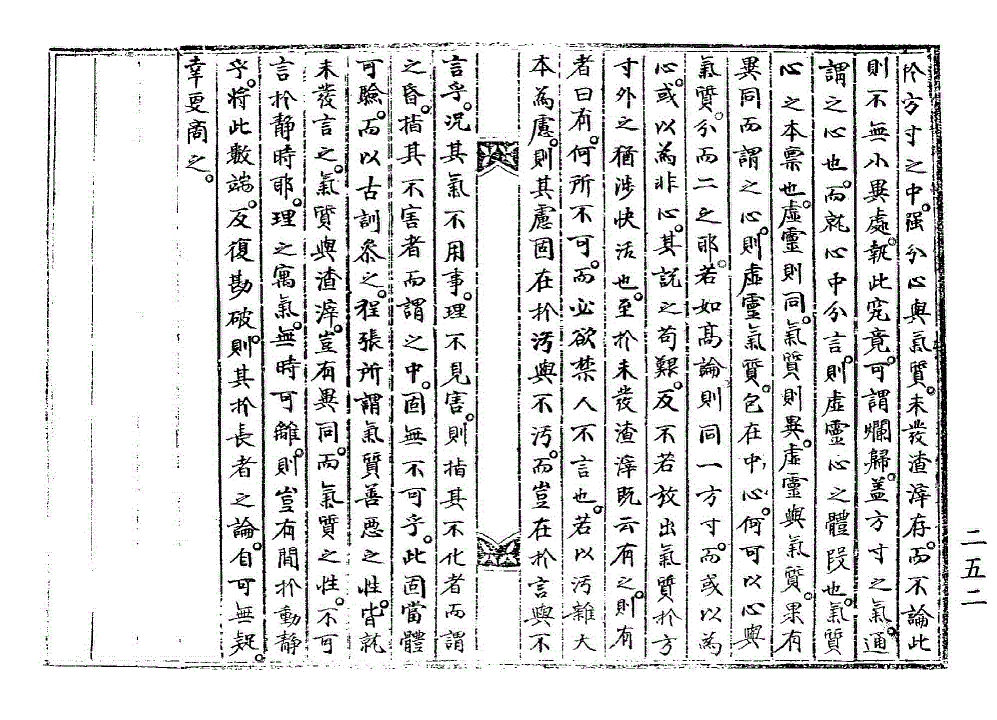 于方寸之中。强分心与气质。未发渣滓存。而不论此则不无小异处。执此究竟。可谓烂归。盖方寸之气。通谓之心也。而就心中分言。则虚灵心之体段也。气质心之本禀也。虚灵则同。气质则异。虚灵与气质。果有异同而谓之心。则虚灵气质。包在心中。何可以心与气质。分而二之耶。若如高论。则同一方寸。而或以为心。或以为非心。其说之苟艰。反不若放出气质于方寸外之犹涉快活也。至于未发渣滓既云有之。则有者曰有。何所不可。而必欲禁人不言也。若以污杂大本为虑。则其虑固在于污与不污。而岂在于言与不言乎。况其气不用事。理不见害。则指其不化者而谓之昏。指其不害者而谓之中。固无不可乎。此固当体可验。而以古训参之。程张所谓气质善恶之性。皆就未发言之。气质与渣滓。岂有异同。而气质之性。不可言于静时耶。理之寓气。无时可离。则岂有间于动静乎。将此数端。反复勘破。则其于长者之论。自可无疑。幸更商之。
于方寸之中。强分心与气质。未发渣滓存。而不论此则不无小异处。执此究竟。可谓烂归。盖方寸之气。通谓之心也。而就心中分言。则虚灵心之体段也。气质心之本禀也。虚灵则同。气质则异。虚灵与气质。果有异同而谓之心。则虚灵气质。包在心中。何可以心与气质。分而二之耶。若如高论。则同一方寸。而或以为心。或以为非心。其说之苟艰。反不若放出气质于方寸外之犹涉快活也。至于未发渣滓既云有之。则有者曰有。何所不可。而必欲禁人不言也。若以污杂大本为虑。则其虑固在于污与不污。而岂在于言与不言乎。况其气不用事。理不见害。则指其不化者而谓之昏。指其不害者而谓之中。固无不可乎。此固当体可验。而以古训参之。程张所谓气质善恶之性。皆就未发言之。气质与渣滓。岂有异同。而气质之性。不可言于静时耶。理之寓气。无时可离。则岂有间于动静乎。将此数端。反复勘破。则其于长者之论。自可无疑。幸更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