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x 页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筵说
筵说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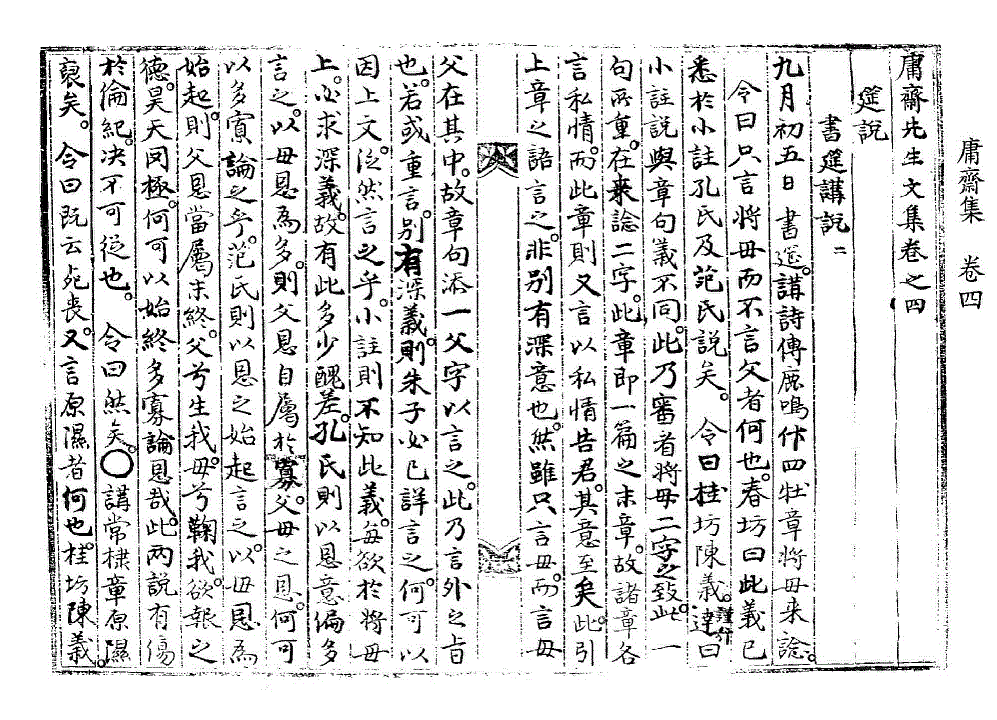 书筵讲说(二)
书筵讲说(二)九月初五日 书筵。讲诗传鹿鸣什四牡章将母来谂。 令曰只言将母而不言父者何也。春坊曰此义已悉于小注孔氏及范氏说矣。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小注说与章句义不同。此乃审看将母二字之致。此一句所重。在来谂二字。此章即一篇之末章。故诸章各言私情。而此章则又言以私情告君。其意至矣。此引上章之语言之。非别有深意也。然虽只言母。而言母父在其中。故章句添一父字以言之。此乃言外之旨也。若或重言。别有深义。则朱子必已详言之。何可以因上文。泛然言之乎。小注则不知此义。每欲于将母上。必求深义。故有此多少丑差。孔氏则以恩意偏多言之。以母恩为多。则父恩自属于寡。父母之恩。何可以多寡论之乎。范氏则以恩之始起言之。以母恩为始起。则父恩当属末终。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何可以始终多寡论恩哉。此两说有伤于伦纪。决不可从也。 令曰然矣。○讲常棣章原隰裒矣。 令曰既云死丧。又言原隰者何也。桂坊陈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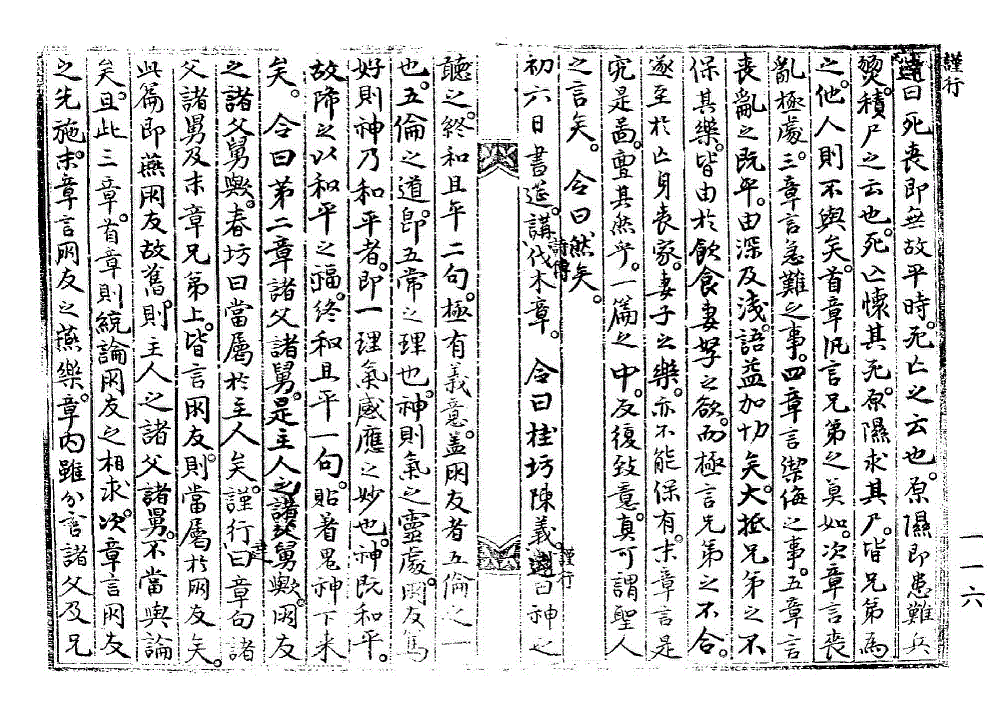 谨行达曰死丧即无故平时。死亡之云也。原隰即患难兵燹。积尸之云也。死亡怀其死。原隰求其尸。皆兄弟为之。他人则不与矣。首章汎言兄弟之莫如。次章言丧乱极处。三章言急难之事。四章言御侮之事。五章言丧乱之既平。由深及浅。语益加切矣。大抵兄弟之不保其乐。皆由于饮食妻孥之欲。而极言兄弟之不合。遂至于亡身丧家。妻子之乐。亦不能保有。末章言是究是啚。亶其然乎。一篇之中。反复致意。真可谓圣人之言矣。 令曰然矣。
谨行达曰死丧即无故平时。死亡之云也。原隰即患难兵燹。积尸之云也。死亡怀其死。原隰求其尸。皆兄弟为之。他人则不与矣。首章汎言兄弟之莫如。次章言丧乱极处。三章言急难之事。四章言御侮之事。五章言丧乱之既平。由深及浅。语益加切矣。大抵兄弟之不保其乐。皆由于饮食妻孥之欲。而极言兄弟之不合。遂至于亡身丧家。妻子之乐。亦不能保有。末章言是究是啚。亶其然乎。一篇之中。反复致意。真可谓圣人之言矣。 令曰然矣。初六日书筵。讲诗传伐木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二句。极有义意。盖朋友者五伦之一也。五伦之道。即五常之理也。神则气之灵处。朋友笃好则神乃和平者。即一理气感应之妙也。神既和平。故降之以和平之福。终和且平一句。贴着鬼神下来矣。 令曰第二章诸父诸舅。是主人之诸父舅欤。朋友之诸父舅欤。春坊曰当属于主人矣。谨行达曰章句诸父诸舅及末章兄弟上。皆言朋友。则当属于朋友矣。此篇即燕朋友故旧。则主人之诸父诸舅。不当与论矣。且此三章。首章则统论朋友之相求。次章言朋友之先施。末章言朋友之燕乐。章内虽分言诸父及兄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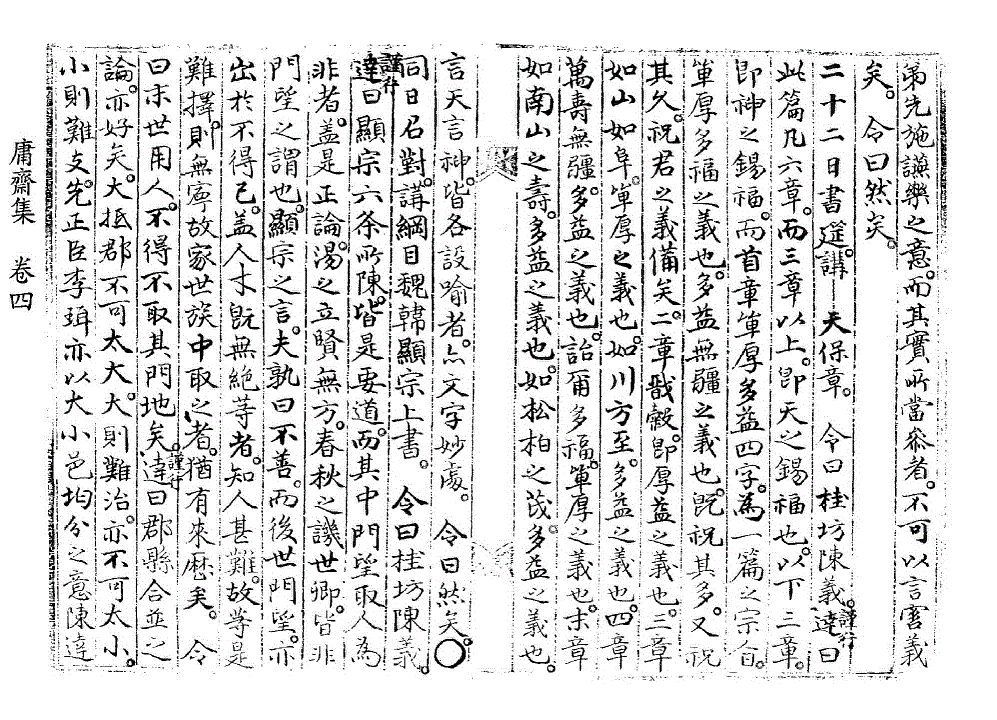 弟先施宴乐之意。而其实所当参看。不可以言害义矣。 令曰然矣。
弟先施宴乐之意。而其实所当参看。不可以言害义矣。 令曰然矣。二十二日书筵。讲天保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此篇凡六章。而三章以上。即天之锡福也。以下三章。即神之锡福。而首章单厚多益四字。为一篇之宗旨。单厚多福之义也。多益无疆之义也。既祝其多。又祝其久。祝君之义备矣。二章戬谷。即厚益之义也。三章如山如阜。单厚之义也。如川方至。多益之义也。四章万寿无疆。多益之义也。诒尔多福。单厚之义也。末章如南山之寿。多益之义也。如松柏之茂。多益之义也。言天言神。皆各设喻者。亦文字妙处。 令曰然矣。○同日召对。讲纲目魏韩显宗上书。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显宗六条所陈。皆是要道。而其中门望取人为非者。盖是正论。汤之立贤无方。春秋之讥世卿。皆非门望之谓也。显宗之言。夫孰曰不善。而后世门望。亦出于不得已。盖人才既无绝等者。知人甚难。故等是难择。则无宁故家世族中取之者。犹有来历矣。 令曰末世用人。不得不取其门地矣。谨行达曰郡县合并之论。亦好矣。大抵郡不可太大。大则难治。亦不可太小。小则难支。先正臣李珥亦以大小邑均分之意陈达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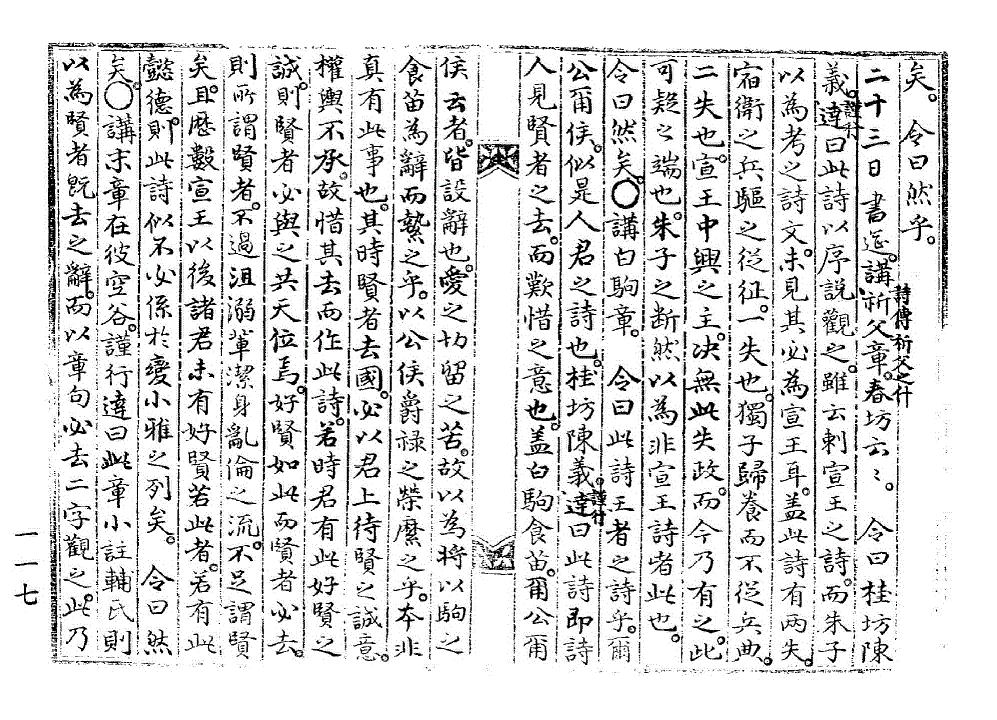 矣。 令曰然乎。
矣。 令曰然乎。二十三日 书筵。讲诗传祈父之什祈父章。春坊云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此诗以序说观之。虽云刺宣王之诗。而朱子以为考之诗文。未见其必为宣王耳。盖此诗有两失。宿卫之兵驱之从征。一失也。独子归养而不从兵典。二失也。宣王中兴之主。决无此失政。而今乃有之。此可疑之端也。朱子之断然以为非宣王诗者此也。 令曰然矣。○讲白驹章。 令曰此诗王者之诗乎。尔公尔侯。似是人君之诗也。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此诗即诗人见贤者之去。而叹惜之意也。盖白驹食苗。尔公尔侯云者。皆设辞也。爱之切留之苦。故以为将以驹之食苗为辞而絷之乎。以公侯爵禄之荣縻之乎。本非真有此事也。其时贤者去国。必以君上待贤之诚意。权舆不承。故惜其去而作此诗。若时君有此好贤之诚。则贤者必与之共天位焉。好贤如此而贤者必去。则所谓贤者。不过沮溺辈洁身乱伦之流。不足谓贤矣。且历数宣王以后诸君未有好贤若此者。若有此懿德。则此诗似不必系于变小雅之列矣。 令曰然矣。○讲末章在彼空谷。谨行达曰此章小注辅氏则以为贤者既去之辞。而以章句必去二字观之。此乃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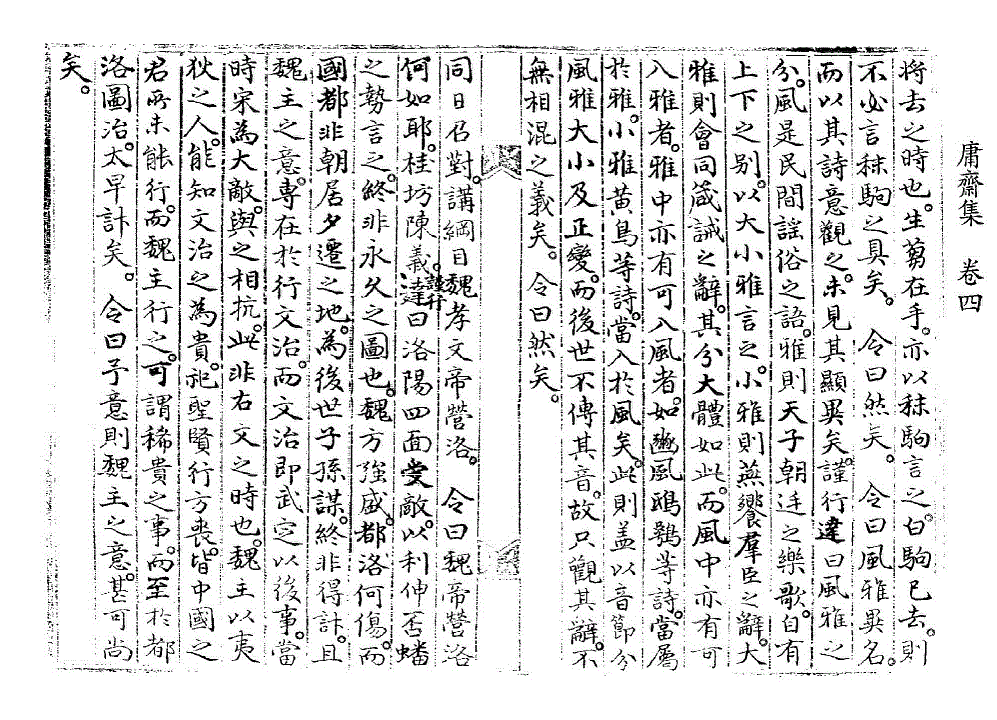 将去之时也。生刍在手。亦以秣驹言之。白驹已去。则不必言秣驹之具矣。 令曰然矣。 令曰风雅异名。而以其诗意观之。未见其显异矣。谨行达曰风雅之分。风是民间谣俗之语。雅则天子朝廷之乐歌。自有上下之别。以大小雅言之。小雅则燕飨群臣之辞。大雅则会同箴诫之辞。其分大体如此。而风中亦有可入雅者。雅中亦有可入风者。如豳风鸱鹗等诗。当属于雅。小雅黄鸟等诗。当入于风矣。此则盖以音节分风雅大小及正变。而后世不传其音。故只观其辞。不无相混之义矣。 令曰然矣。
将去之时也。生刍在手。亦以秣驹言之。白驹已去。则不必言秣驹之具矣。 令曰然矣。 令曰风雅异名。而以其诗意观之。未见其显异矣。谨行达曰风雅之分。风是民间谣俗之语。雅则天子朝廷之乐歌。自有上下之别。以大小雅言之。小雅则燕飨群臣之辞。大雅则会同箴诫之辞。其分大体如此。而风中亦有可入雅者。雅中亦有可入风者。如豳风鸱鹗等诗。当属于雅。小雅黄鸟等诗。当入于风矣。此则盖以音节分风雅大小及正变。而后世不传其音。故只观其辞。不无相混之义矣。 令曰然矣。同日召对。讲纲目魏孝文帝营洛。 令曰魏帝营洛何如耶。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洛阳四面受敌。以利伸否蟠之势言之。终非永久之图也。魏方强盛。都洛何伤。而国都非朝居夕迁之地。为后世子孙谋。终非得计。且魏主之意。专在于行文治。而文治即武定以后事。当时宋为大敌。与之相抗。此非右文之时也。魏主以夷狄之人。能知文治之为贵。祀圣贤行方丧。皆中国之君所未能行。而魏主行之。可谓稀贵之事。而至于都洛图治。太早计矣。 令曰予意则魏主之意。甚可尚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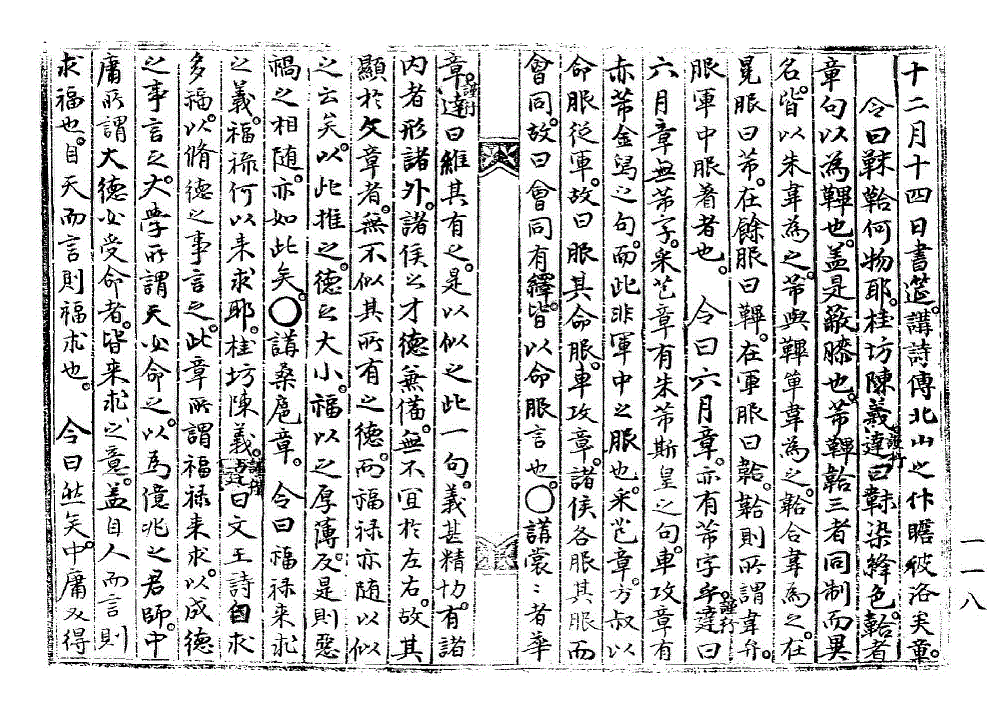 十二月十四日书筵。讲诗传北山之什瞻彼洛矣章。 令曰靺鞈何物耶。桂坊陈义。谨行达曰韎染绛色。韐者章句以为鞸也。盖是蔽膝也。芾鞸韐三者同制而异名。皆以朱韦为之。芾与鞸单韦为之。韐合韦为之。在冕服曰芾。在馀服曰鞸。在军服曰韐。韐则所谓韦弁。服军中服着者也。 令曰六月章。亦有芾字乎。谨行达曰六月章无芾字。采芑章有朱芾斯皇之句。车攻章有赤芾金舄之句。而此非军中之服也。采芑章。方叔以命服从军。故曰服其命服。车攻章。诸侯各服其服而会同。故曰会同有绎。皆以命服言也。○讲裳裳者华章。谨行达曰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一句。义甚精切。有诸内者形诸外。诸侯之才德兼备。无不宜于左右。故其显于文章者。无不似其所有之德。而福禄亦随以似之云矣。以此推之。德之大小。福以之厚薄。反是则恶祸之相随。亦如此矣。○讲桑扈章。 令曰福禄来求之义。福禄何以来求耶。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文王诗自求多福。以脩德之事言之。此章所谓福禄来求。以成德之事言之。大学所谓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中庸所谓大德必受命者。皆来求之意。盖自人而言则求福也。自天而言则福求也。 令曰然矣。中庸必得
十二月十四日书筵。讲诗传北山之什瞻彼洛矣章。 令曰靺鞈何物耶。桂坊陈义。谨行达曰韎染绛色。韐者章句以为鞸也。盖是蔽膝也。芾鞸韐三者同制而异名。皆以朱韦为之。芾与鞸单韦为之。韐合韦为之。在冕服曰芾。在馀服曰鞸。在军服曰韐。韐则所谓韦弁。服军中服着者也。 令曰六月章。亦有芾字乎。谨行达曰六月章无芾字。采芑章有朱芾斯皇之句。车攻章有赤芾金舄之句。而此非军中之服也。采芑章。方叔以命服从军。故曰服其命服。车攻章。诸侯各服其服而会同。故曰会同有绎。皆以命服言也。○讲裳裳者华章。谨行达曰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一句。义甚精切。有诸内者形诸外。诸侯之才德兼备。无不宜于左右。故其显于文章者。无不似其所有之德。而福禄亦随以似之云矣。以此推之。德之大小。福以之厚薄。反是则恶祸之相随。亦如此矣。○讲桑扈章。 令曰福禄来求之义。福禄何以来求耶。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文王诗自求多福。以脩德之事言之。此章所谓福禄来求。以成德之事言之。大学所谓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中庸所谓大德必受命者。皆来求之意。盖自人而言则求福也。自天而言则福求也。 令曰然矣。中庸必得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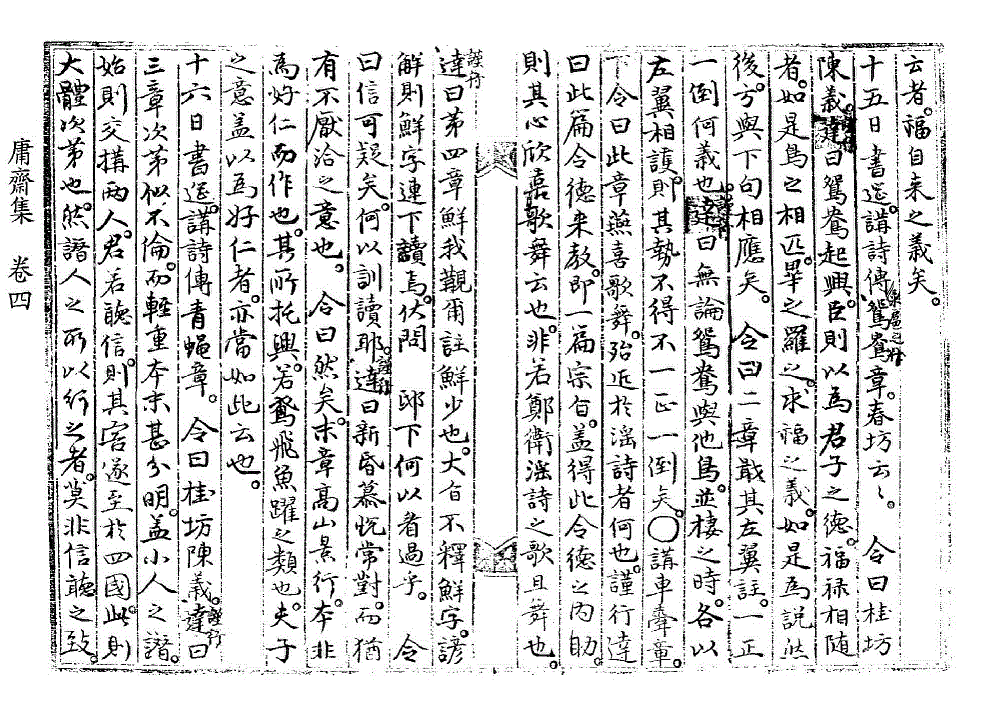 云者。福自来之义矣。
云者。福自来之义矣。十五日书筵。讲诗传桑扈之什鸳鸯章。春坊云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鸳鸯起兴。臣则以为君子之德。福禄相随者。如是鸟之相匹。毕之罗之。求福之义。如是为说然后。方与下句相应矣。 令曰二章戢其左翼注。一正一倒何义也。谨行达曰无论鸳鸯与他鸟。并栖之时。各以左翼相护。则其势不得不一正一倒矣。○讲车辖章。下令曰此章燕喜歌舞。殆近于淫诗者何也。谨行达曰此篇令德来教。即一篇宗旨。盖得此令德之内助。则其心欣喜歌舞云也。非若郑卫淫诗之歌且舞也。谨行达曰第四章鲜我觏尔注鲜少也。大旨不释鲜字。谚解则鲜字连下读焉。伏问 邸下何以看过乎。 令曰信可疑矣。何以训读耶。谨行达曰新昏慕悦常对。而犹有不厌洽之意也。 令曰然矣。末章高山景行。本非为好仁而作也。其所托兴。若鸢飞鱼跃之类也。夫子之意盖以为好仁者。亦当如此云也。
十六日书筵。讲诗传青蝇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三章次第似不伦。而轻重本末甚分明。盖小人之谮。始则交搆两人。君若听信。则其害遂至于四国。此则大体次第也。然谮人之所以行之者。莫非信听之致。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1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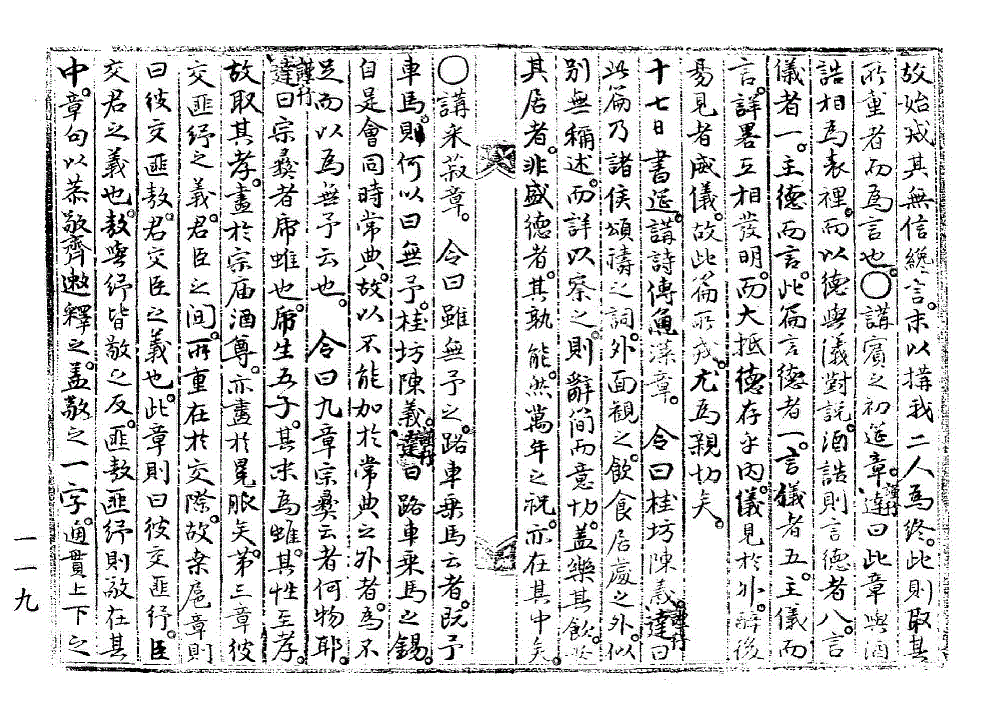 故始戒其无信才言。末以搆我二人为终。此则取其所重者而为言也。○讲宾之初筵章。谨行达曰此章与酒诰相为表里。而以德与仪对说。酒诰则言德者八。言仪者一。主德而言。此篇言德者一。言仪者五。主仪而言。详略互相发明。而大抵德存乎内。仪见于外。醉后易见者威仪。故此篇所戎。尤为亲切矣。
故始戒其无信才言。末以搆我二人为终。此则取其所重者而为言也。○讲宾之初筵章。谨行达曰此章与酒诰相为表里。而以德与仪对说。酒诰则言德者八。言仪者一。主德而言。此篇言德者一。言仪者五。主仪而言。详略互相发明。而大抵德存乎内。仪见于外。醉后易见者威仪。故此篇所戎。尤为亲切矣。十七日书筵。讲诗传鱼藻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此篇乃诸侯颂祷之词。外面观之。饮食居处之外。似别无称述。而详以察之。则辞简而意切。盖乐其饮。安其居者。非盛德者。其孰能。然万年之祝。亦在其中矣。○讲采菽章。 令曰虽无予之。路车乘马云者。既予车马。则何以曰无予。桂坊陈义。谨行达曰路车乘马之锡。自是会同时常典。故以不能加于常典之外者。为不足而以为无予云也。 令曰九章宗彝云者何物耶。谨行达曰宗彝者虎蜼也。虎生五子。其末为蜼。其性至孝。故取其孝。画于宗庙酒尊。亦画于冕服矣。第三章彼交匪纾之义。君臣之间。所重在于交际。故桑扈章则曰彼交匪敖。君交臣之义也。此章则曰彼交匪纾。臣交君之义也。敖与纾皆敬之反。匪敖匪纾则敬在其中。章句以恭敬齐遫释之。盖敬之一字。通贯上下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0H 页
 义。亦可见矣。 令曰偪制何如。谨行达曰偪制以注释观之。则即今之缠。行縢也。以邪幅自足腂缠之。至胫而止。幅端有两小系。系于膝骨下者。以啚子观之。全幅上下。各有两系。上系于胫。下系于腂。与此注差异。而偪亦有两制而然尔。此章盛言诸侯之德。而第三章言天子命之。第五章言天子葵之。葵者度也。能度诸侯之心。知其底蕴也。以是结之者。其意亦深切矣。
义。亦可见矣。 令曰偪制何如。谨行达曰偪制以注释观之。则即今之缠。行縢也。以邪幅自足腂缠之。至胫而止。幅端有两小系。系于膝骨下者。以啚子观之。全幅上下。各有两系。上系于胫。下系于腂。与此注差异。而偪亦有两制而然尔。此章盛言诸侯之德。而第三章言天子命之。第五章言天子葵之。葵者度也。能度诸侯之心。知其底蕴也。以是结之者。其意亦深切矣。辛卯正月十八日书筵。讲诗传大雅生民篇板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变大雅以民劳为首。大凡变诗自风为始。必以处变得正者为首篇。民劳诗厉王之时。政衰国乱。同列大夫忧时感事。相与箴戒。以及于君。盖得情性之正者也。板章亦与民劳同意。其相戒之辞恳到切实。比民劳尤为至极矣。一篇宗旨。归重于德之一字。而诚敬二字。为其羽翼。诚与敬相对而言之。则二者各有体用。相包而言。则诚为体而敬为用。诚为德之体。敬为德之用也。故首言诚。亶字即诚也。末章言敬。中言德。其义备矣。敬天之天。以形体言。张子所言天字。以义理言。所主而言者不同。出往游衍。皆以动处言之。而以小注戒惧慎独之说观之。盖是兼动静言矣。 令曰其言好矣。昊天无处不随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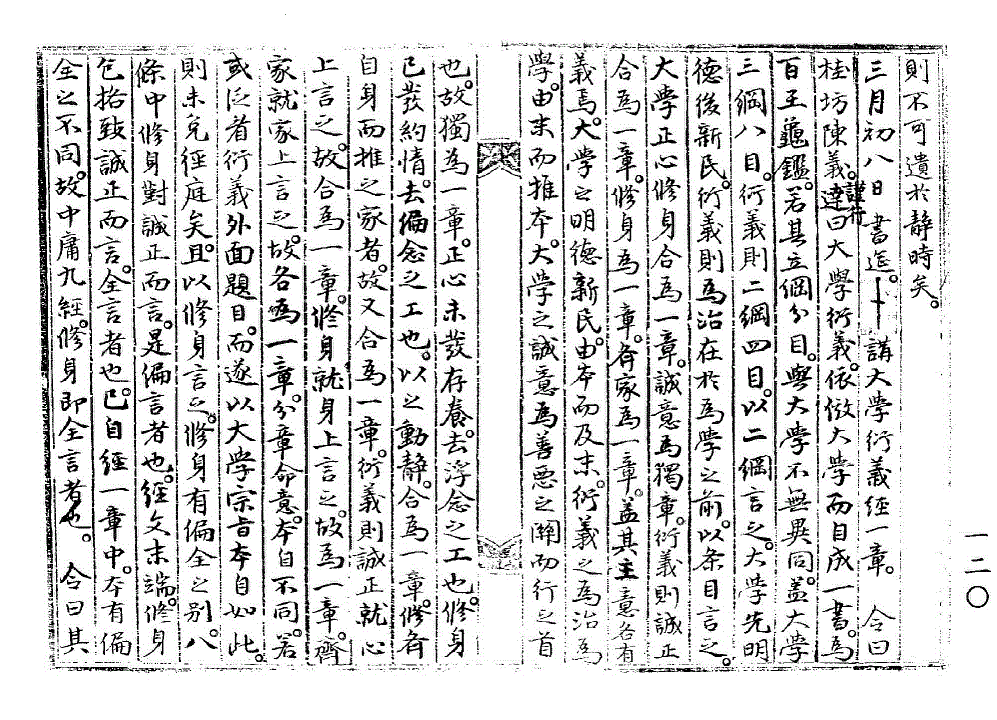 则不可遗于静时矣。
则不可遗于静时矣。三月初八日书筵。讲大学衍义经一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大学衍义。依仿大学而自成一书。为百王龟鉴。若其立纲分目。与大学不无异同。盖大学三纲八目。衍义则二纲四目。以二纲言之。大学先明德后新民。衍义则为治在于为学之前。以条目言之。大学正心修身合为一章。诚意为独章。衍义则诚正合为一章。修身为一章。齐家为一章。盖其主意各有义焉。大学之明德新民。由本而及末。衍义之为治为学。由末而推本。大学之诚意为善恶之关而行之首也。故独为一章。正心未发存养。去浮念之工也。修身已发约情。去偏念之工也。以之动静。合为一章。修齐自身而推之家者。故又合为一章。衍义则诚正就心上言之。故合为一章。修身就身上言之。故为一章。齐家就家上言之。故各为一章。分章命意。本自不同。若或泛看衍义外面题目。而遂以大学宗旨本自如此。则未免径庭矣。且以修身言之。修身有偏全之别。八条中修身对诚正而言。是偏言者也。经文末端。修身包格致诚正而言。全言者也。已自经一章中。本有偏全之不同。故中庸九经。修身即全言者也。 令曰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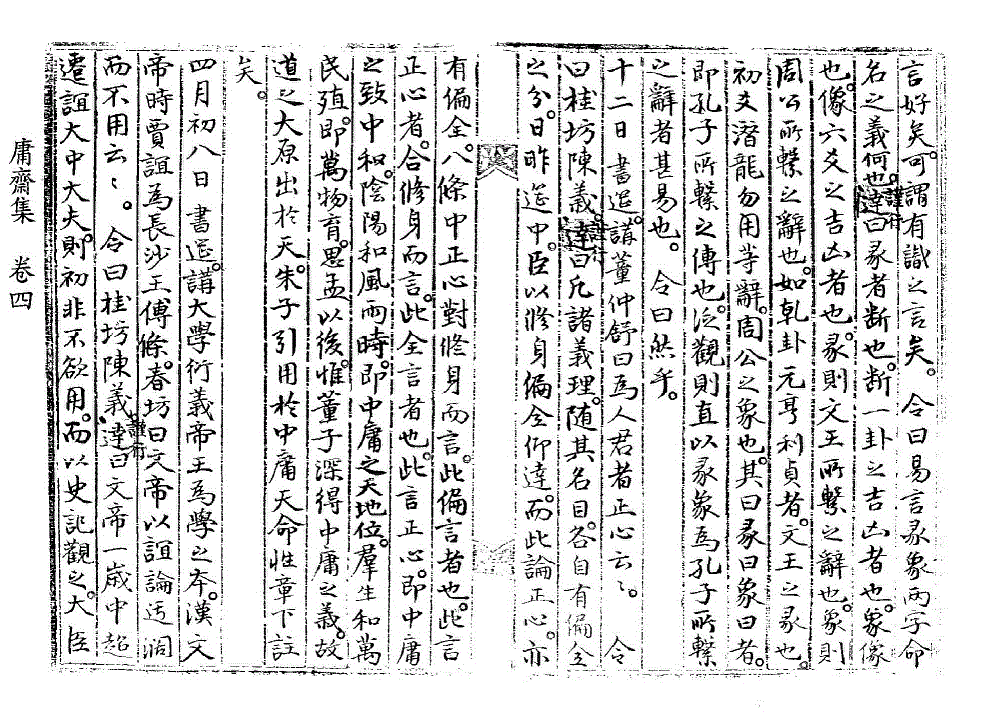 言好矣。可谓有识之言矣。 令曰易言彖象两字命名之义何也。谨行达曰彖者断也。断一卦之吉凶者也。象像也。像六爻之吉凶者也。彖则文王所系之辞也。象则周公所系之辞也。如乾卦元亨利贞者。文王之彖也。初爻潜龙勿用等辞。周公之象也。其曰彖曰象曰者。即孔子所系之传也。泛观则直以彖象为孔子所系之辞者甚易也。 令曰然乎。
言好矣。可谓有识之言矣。 令曰易言彖象两字命名之义何也。谨行达曰彖者断也。断一卦之吉凶者也。象像也。像六爻之吉凶者也。彖则文王所系之辞也。象则周公所系之辞也。如乾卦元亨利贞者。文王之彖也。初爻潜龙勿用等辞。周公之象也。其曰彖曰象曰者。即孔子所系之传也。泛观则直以彖象为孔子所系之辞者甚易也。 令曰然乎。十二日书筵。讲董仲舒曰为人君者正心云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凡诸义理。随其名目。各自有偏全之分。日昨筵中。臣以修身偏全仰达。而此论正心。亦有偏全。八条中正心对修身而言。此偏言者也。此言正心者。合修身而言。此全言者也。此言正心。即中庸之致中和。阴阳和风雨时。即中庸之天地位。群生和万民殖。即万物育。思孟以后。惟董子深得中庸之义。故道之大原出于天。朱子引用于中庸天命性章下注矣。
四月初八日书筵。讲大学衍义帝王为学之本。汉文帝时贾谊为长沙王傅条。春坊曰文帝以谊论迂阔而不用云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文帝一岁中超迁谊大中大夫。则初非不欲用。而以史记观之。大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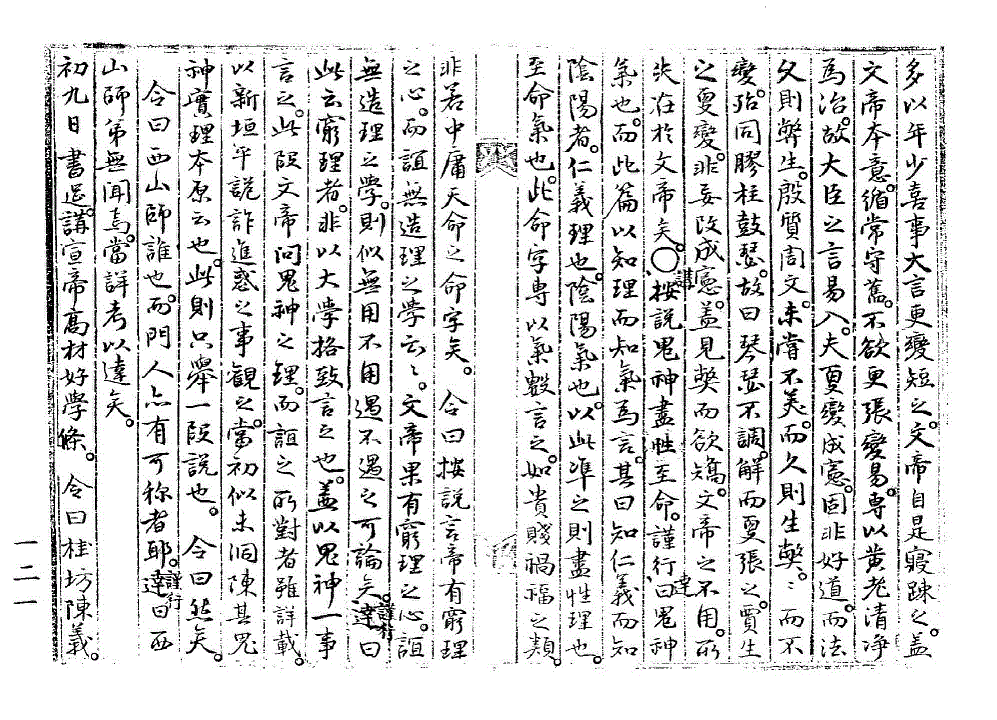 多以年少喜事大言更变短之。文帝自是寝疏之。盖文帝本意。循常守旧。不欲更张变易。专以黄老清净为治。故大臣之言易入。夫更变成宪。固非好道。而法久则弊生。殷质周文。未尝不美。而久则生弊。弊而不变。殆同胶柱鼓瑟。故曰琴瑟不调。解而更张之。贾生之更变。非妄改成宪。盖见弊而欲矫。文帝之不用。所失在于文帝矣。○讲按说鬼神尽性至命。谨行达曰鬼神气也。而此篇以知理而知气为言。其曰知仁义而知阴阳者。仁义理也。阴阳气也。以此准之则尽性理也。至命气也。此命字专以气数言之。如贵贱祸福之类。非若中庸天命之命字矣。 令曰按说言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云云。文帝果有穷理之心。谊无造理之学。则似无用不用遇不遇之可论矣。谨行达曰此云穷理者。非以大学格致言之也。盖以鬼神一事言之。此段文帝问鬼神之理。而谊之所对者虽详载。以新垣平诡诈进惑之事观之。当初似未洞陈其鬼神实理本原云也。此则只举一段说也。 令曰然矣。 令曰西山师谁也。而门人亦有可称者耶。谨行达曰西山师弟无闻焉。当详考以达矣。
多以年少喜事大言更变短之。文帝自是寝疏之。盖文帝本意。循常守旧。不欲更张变易。专以黄老清净为治。故大臣之言易入。夫更变成宪。固非好道。而法久则弊生。殷质周文。未尝不美。而久则生弊。弊而不变。殆同胶柱鼓瑟。故曰琴瑟不调。解而更张之。贾生之更变。非妄改成宪。盖见弊而欲矫。文帝之不用。所失在于文帝矣。○讲按说鬼神尽性至命。谨行达曰鬼神气也。而此篇以知理而知气为言。其曰知仁义而知阴阳者。仁义理也。阴阳气也。以此准之则尽性理也。至命气也。此命字专以气数言之。如贵贱祸福之类。非若中庸天命之命字矣。 令曰按说言帝有穷理之心。而谊无造理之学云云。文帝果有穷理之心。谊无造理之学。则似无用不用遇不遇之可论矣。谨行达曰此云穷理者。非以大学格致言之也。盖以鬼神一事言之。此段文帝问鬼神之理。而谊之所对者虽详载。以新垣平诡诈进惑之事观之。当初似未洞陈其鬼神实理本原云也。此则只举一段说也。 令曰然矣。 令曰西山师谁也。而门人亦有可称者耶。谨行达曰西山师弟无闻焉。当详考以达矣。初九日书筵。讲宣帝高材好学条。 令曰桂坊陈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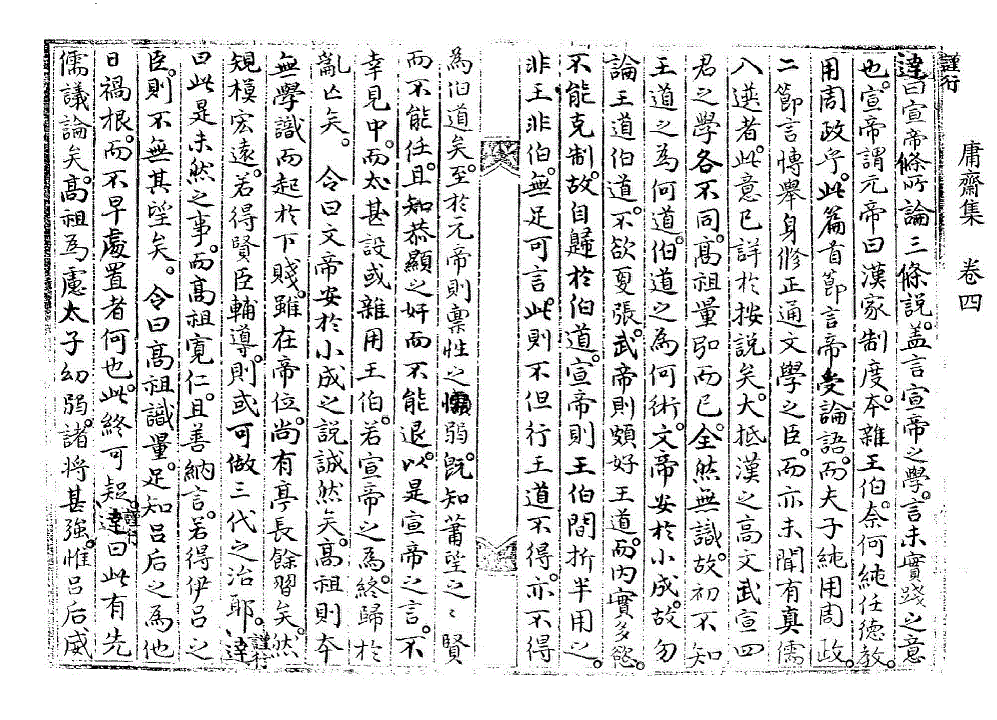 谨行达曰宣帝条所论三条说。盖言宣帝之学。言未实践之意也。宣帝谓元帝曰汉家制度。本杂王伯。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此篇首节言帝受论语。而夫子纯用周政。二节言博举身修正通文学之臣。而亦未闻有真儒入选者。此意已详于按说矣。大抵汉之高文武宣四君之学各不同。高祖量弘而已。全然无识。故初不知王道之为何道。伯道之为何术。文帝安于小成。故勿论王道伯道。不欲更张。武帝则颇好王道。而内实多欲。不能克制。故自归于伯道。宣帝则王伯间折半用之。非王非伯。无足可言。此则不但行王道不得。亦不得为伯道矣。至于元帝则禀性之懦弱。既知萧望之之贤而不能任。且知恭显之奸而不能退。以是宣帝之言。不幸见中。而甚太设或杂用王伯。若宣帝之为。终归于乱亡矣。 令曰文帝安于小成之说诚然矣。高祖则本无学识而起于下贱。虽在帝位。尚有亭长馀习矣。然规模宏远。若得贤臣辅导。则或可做三代之治耶。谨行达曰此是未然之事。而高祖宽仁。且善纳言。若得伊吕之臣。则不无其望矣。 令曰高祖识量。足知吕后之为他日祸根。而不早处置者何也。此终可疑。谨行达曰此有先儒议论矣。高祖为虑太子幼弱。诸将甚强。惟吕后威
谨行达曰宣帝条所论三条说。盖言宣帝之学。言未实践之意也。宣帝谓元帝曰汉家制度。本杂王伯。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此篇首节言帝受论语。而夫子纯用周政。二节言博举身修正通文学之臣。而亦未闻有真儒入选者。此意已详于按说矣。大抵汉之高文武宣四君之学各不同。高祖量弘而已。全然无识。故初不知王道之为何道。伯道之为何术。文帝安于小成。故勿论王道伯道。不欲更张。武帝则颇好王道。而内实多欲。不能克制。故自归于伯道。宣帝则王伯间折半用之。非王非伯。无足可言。此则不但行王道不得。亦不得为伯道矣。至于元帝则禀性之懦弱。既知萧望之之贤而不能任。且知恭显之奸而不能退。以是宣帝之言。不幸见中。而甚太设或杂用王伯。若宣帝之为。终归于乱亡矣。 令曰文帝安于小成之说诚然矣。高祖则本无学识而起于下贱。虽在帝位。尚有亭长馀习矣。然规模宏远。若得贤臣辅导。则或可做三代之治耶。谨行达曰此是未然之事。而高祖宽仁。且善纳言。若得伊吕之臣。则不无其望矣。 令曰高祖识量。足知吕后之为他日祸根。而不早处置者何也。此终可疑。谨行达曰此有先儒议论矣。高祖为虑太子幼弱。诸将甚强。惟吕后威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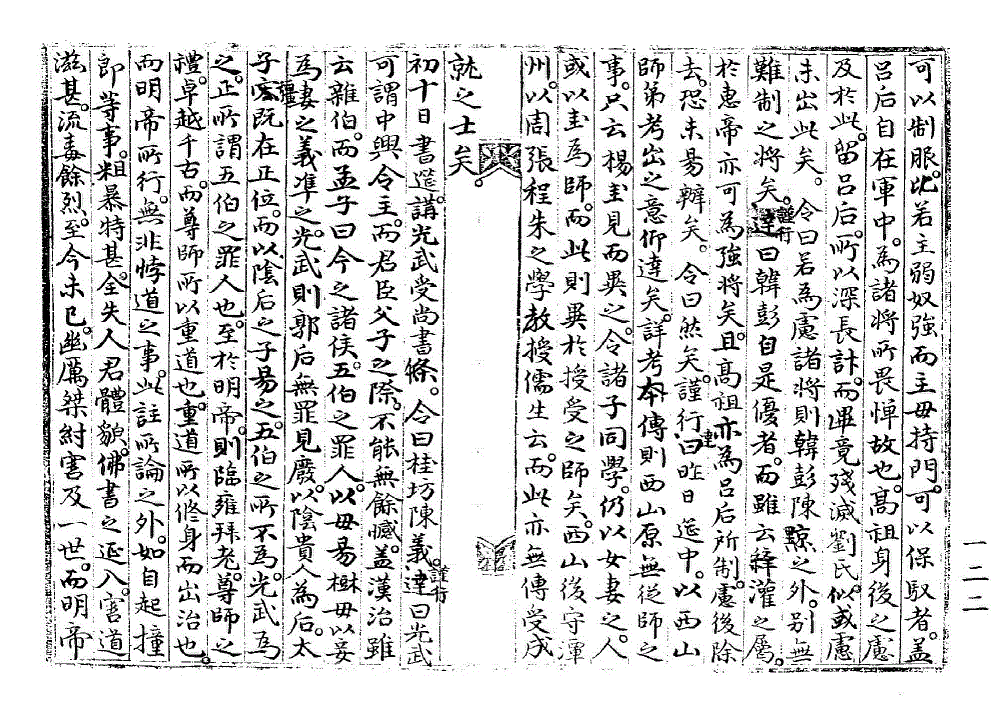 可以制服。比若主弱奴强而主母持门。可以保驭者。盖吕后自在军中。为诸将所畏惮故也。高祖身后之虑及于此。留吕后。所以深长计。而毕竟残灭刘氏。似或虑未出此矣。 令曰若为虑诸将则韩彭陈黥之外。别无难制之将矣。谨行达曰韩彭自是优者。而虽云绛灌之属。于惠帝亦可为强将矣。且高祖亦为吕后所制。虑后除去。恐未易办矣。 令曰然矣。谨行达曰昨日筵中。以西山师弟考出之意仰达矣。详考本传则西山原无从师之事。只云杨圭见而异之。令诸子同学。仍以女妻之。人或以圭为师。而此则异于授受之师矣。西山后守潭州。以周张程朱之学教授儒生云。而此亦无传受成就之士矣。
可以制服。比若主弱奴强而主母持门。可以保驭者。盖吕后自在军中。为诸将所畏惮故也。高祖身后之虑及于此。留吕后。所以深长计。而毕竟残灭刘氏。似或虑未出此矣。 令曰若为虑诸将则韩彭陈黥之外。别无难制之将矣。谨行达曰韩彭自是优者。而虽云绛灌之属。于惠帝亦可为强将矣。且高祖亦为吕后所制。虑后除去。恐未易办矣。 令曰然矣。谨行达曰昨日筵中。以西山师弟考出之意仰达矣。详考本传则西山原无从师之事。只云杨圭见而异之。令诸子同学。仍以女妻之。人或以圭为师。而此则异于授受之师矣。西山后守潭州。以周张程朱之学教授儒生云。而此亦无传受成就之士矣。初十日书筵。讲光武受尚书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光武可谓中兴令主。而君臣父子之际。不能无馀憾。盖汉治虽云杂伯。而孟子曰今之诸侯。五伯之罪人。以毋易树毋以妾为妻之义准之。光武则郭后无罪见废。以阴贵人为后。太子彊既在正位。而以阴后之子易之。五伯之所不为。光武为之。正所谓五伯之罪人也。至于明帝。则临雍拜老。尊师之礼。卓越千古。而尊师所以重道也。重道所以修身而出治也。而明帝所行。无非悖道之事。此注所论之外。如自起撞郎等事。粗暴特甚。全失人君体貌。佛书之延入。害道滋甚。流毒馀烈。至今未已。幽厉桀纣害及一世。而明帝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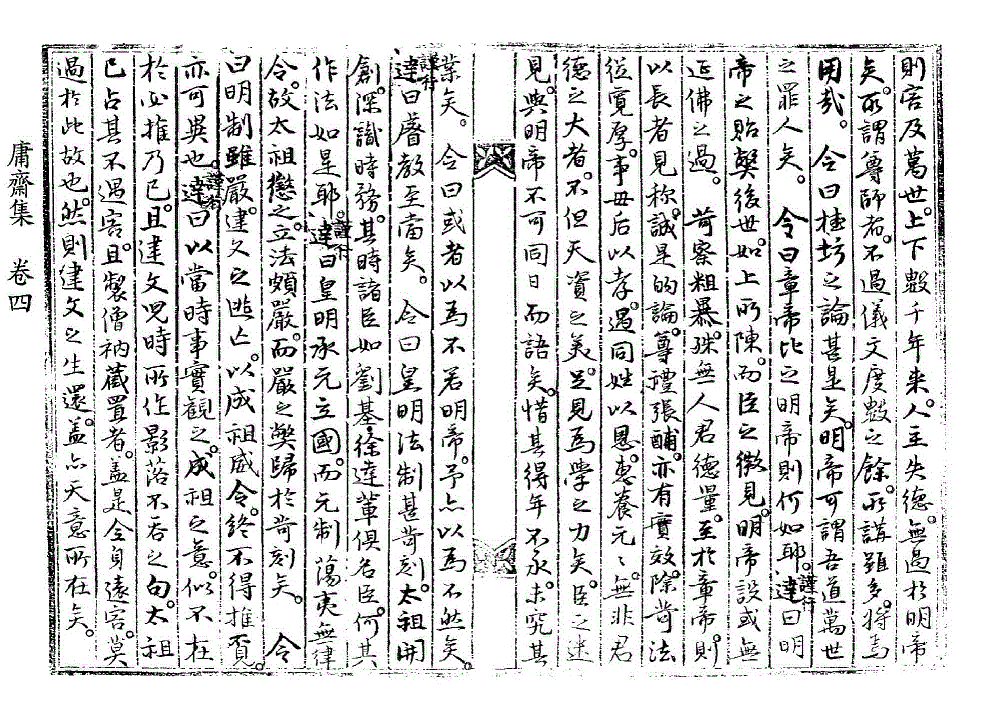 则害及万世。上下数千年来。人主失德。无过于明帝矣。所谓尊师者。不过仪文度数之馀。所讲虽多。将焉用哉。 令曰桂坊之论甚是矣。明帝可谓吾道万世之罪人矣。 令曰章帝比之明帝则何如耶。谨行达曰明帝之贻弊后世。如上所陈。而臣之微见。明帝设或无延佛之过。 苛察粗暴。殊无人君德量。至于章帝。则以长者见称。诚是的论。尊礼张酺。亦有实效。除苛法从宽厚。事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养元元。无非君德之大者。不但天资之美。足见为学之力矣。臣之迷见。与明帝不可同日而语矣。惜其得年不永。未究其业矣。 令曰或者以为不若明帝。予亦以为不然矣。谨行达曰睿教至当矣。 令曰皇明法制甚苛刻。太祖开创。深识时务。其时诸臣如刘基,徐达辈俱名臣。何其作法如是耶。谨行达曰皇明承元立国。而元制荡夷无律令。故太祖惩之。立法颇严。而严之弊归于苛刻矣。 令曰明制虽严。建文之逃亡。以成祖威令。终不得推觅。亦可异也。谨行达曰以当时事实观之。成祖之意。似不在于必推乃已。且建文儿时所作影落不吞之句。太祖已占其不遇害。且制僧衲藏置者。盖是全身远害。莫过于此故也。然则建文之生还。盖亦天意所在矣。
则害及万世。上下数千年来。人主失德。无过于明帝矣。所谓尊师者。不过仪文度数之馀。所讲虽多。将焉用哉。 令曰桂坊之论甚是矣。明帝可谓吾道万世之罪人矣。 令曰章帝比之明帝则何如耶。谨行达曰明帝之贻弊后世。如上所陈。而臣之微见。明帝设或无延佛之过。 苛察粗暴。殊无人君德量。至于章帝。则以长者见称。诚是的论。尊礼张酺。亦有实效。除苛法从宽厚。事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养元元。无非君德之大者。不但天资之美。足见为学之力矣。臣之迷见。与明帝不可同日而语矣。惜其得年不永。未究其业矣。 令曰或者以为不若明帝。予亦以为不然矣。谨行达曰睿教至当矣。 令曰皇明法制甚苛刻。太祖开创。深识时务。其时诸臣如刘基,徐达辈俱名臣。何其作法如是耶。谨行达曰皇明承元立国。而元制荡夷无律令。故太祖惩之。立法颇严。而严之弊归于苛刻矣。 令曰明制虽严。建文之逃亡。以成祖威令。终不得推觅。亦可异也。谨行达曰以当时事实观之。成祖之意。似不在于必推乃已。且建文儿时所作影落不吞之句。太祖已占其不遇害。且制僧衲藏置者。盖是全身远害。莫过于此故也。然则建文之生还。盖亦天意所在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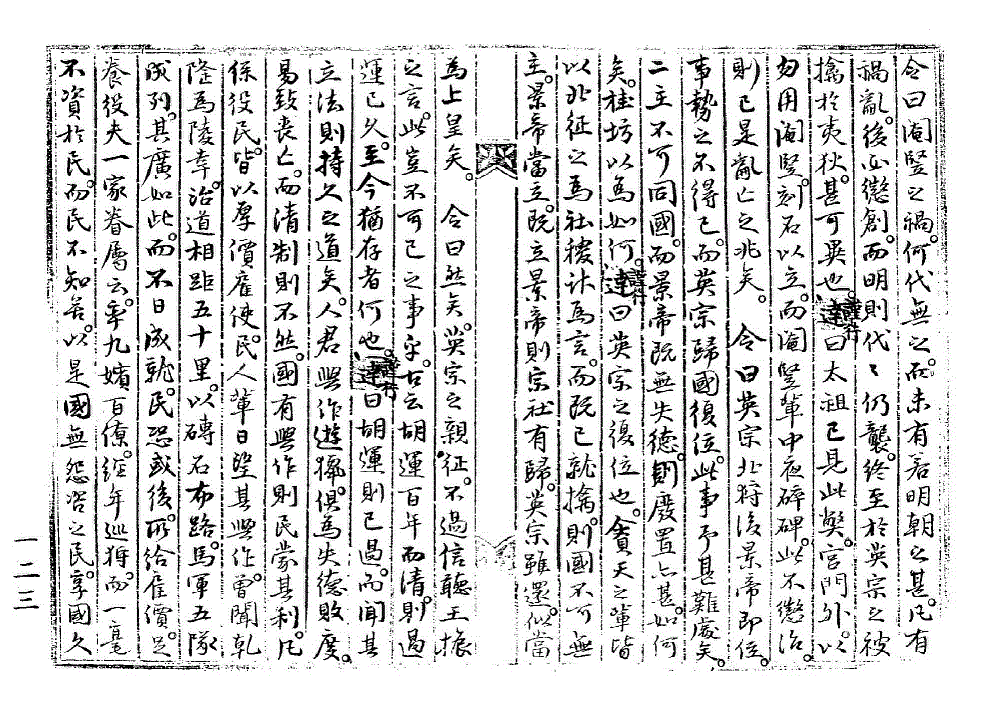 令曰阉竖之祸。何代无之。而未有若明朝之甚。凡有祸乱。后必惩创。而明则代代仍袭。终至于英宗之被擒于夷狄。甚可异也。谨行达曰太祖已见此弊。宫门外。以勿用阉竖。刻石以立。而阉竖辈中夜碎碑。此不惩治。则已是乱亡之兆矣。 令曰英宗北狩后景帝即位。事势之不得已。而英宗归国复位。此事予甚难处矣。二主不可同国。而景帝既无失德。则废置亦甚。如何矣。桂坊以为如何。谨行达曰英宗之复位也。贪天之辈皆以北征之为社稷计为言。而既已就擒。则国不可无主。景帝当立。既立景帝则宗社有归。英宗虽还。似当为上皇矣。 令曰然矣。英宗之亲征。不过信听王振之言。此岂不可已之事乎。古云胡运百年而清。则过运已久。至今犹存者何也。谨行达曰胡运则已过。而闻其立法则持久之道矣。人君兴作游猎。俱为失德败度。易致丧亡。而清制则不然。国有兴作则民蒙其利。凡系役民。皆以厚价雇使。民人辈日望其兴作。曾闻乾隆为陵幸。治道相距五十里。以砖石布路。马军五队成列。其广如此。而不日成就。民恐或后。所给雇价。足养役夫一家眷属云。率九嫔百僚。经年巡狩。而一毫不资于民。而民不知苦。以是国无怨咨之民。享国久
令曰阉竖之祸。何代无之。而未有若明朝之甚。凡有祸乱。后必惩创。而明则代代仍袭。终至于英宗之被擒于夷狄。甚可异也。谨行达曰太祖已见此弊。宫门外。以勿用阉竖。刻石以立。而阉竖辈中夜碎碑。此不惩治。则已是乱亡之兆矣。 令曰英宗北狩后景帝即位。事势之不得已。而英宗归国复位。此事予甚难处矣。二主不可同国。而景帝既无失德。则废置亦甚。如何矣。桂坊以为如何。谨行达曰英宗之复位也。贪天之辈皆以北征之为社稷计为言。而既已就擒。则国不可无主。景帝当立。既立景帝则宗社有归。英宗虽还。似当为上皇矣。 令曰然矣。英宗之亲征。不过信听王振之言。此岂不可已之事乎。古云胡运百年而清。则过运已久。至今犹存者何也。谨行达曰胡运则已过。而闻其立法则持久之道矣。人君兴作游猎。俱为失德败度。易致丧亡。而清制则不然。国有兴作则民蒙其利。凡系役民。皆以厚价雇使。民人辈日望其兴作。曾闻乾隆为陵幸。治道相距五十里。以砖石布路。马军五队成列。其广如此。而不日成就。民恐或后。所给雇价。足养役夫一家眷属云。率九嫔百僚。经年巡狩。而一毫不资于民。而民不知苦。以是国无怨咨之民。享国久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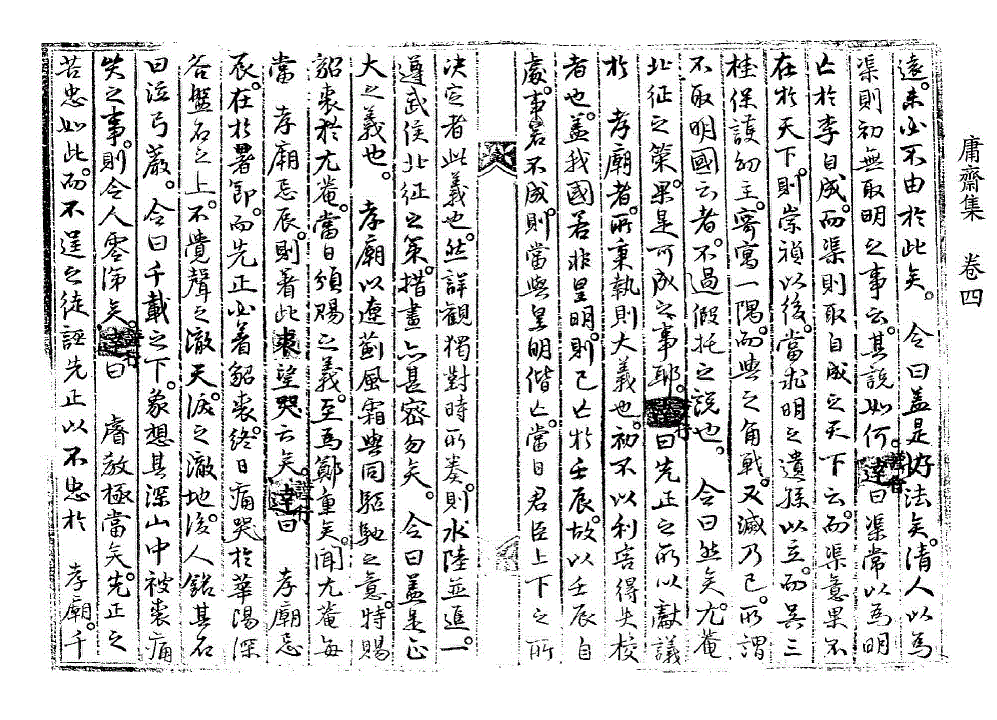 远。未必不由于此矣。 令曰盖是好法矣。清人以为渠则初无取明之事云。其说如何。谨行达曰渠常以为明亡于李自成。而渠则取自成之天下云。而渠意果不在于天下。则崇祯以后。当求明之遗孙以立。而吴三桂保护幼主。寄寓一隅。而与之角战。必灭乃已。所谓不取明国云者。不过假托之说也。 令曰然矣。尤庵北征之策。果是可成之事耶。谨行达曰先正之所以献议于 孝庙者。所秉执则大义也。初不以利害得失校者也。盖我国若非皇明。则已亡于壬辰。故以壬辰自处。事若不成。则当与皇明偕亡。当日君臣上下之所决定者此义也。然详观独对时所奏。则水陆并进。一遵武侯北征之策。措画亦甚密勿矣。 令曰盖是正大之义也。 孝庙以辽蓟风霜与同驱驰之意。特赐貂裘于尤庵。当日颁赐之义。至为郑重矣。闻尤庵每当 孝庙忌辰。则着此裘望哭云矣。谨行达曰 孝庙忌辰。在于暑节。而先正必着貂裘。终日痛哭于华阳深谷盘石之上。不觉声之澈天。泪之澈地。后人铭其石曰泣弓岩。 令曰千载之下。象想其深山中被裘痛哭之事。则令人零涕矣。谨行达曰 睿教极当矣。先正之苦忠如此。而不逞之徒诬先正以不忠于 孝庙。千
远。未必不由于此矣。 令曰盖是好法矣。清人以为渠则初无取明之事云。其说如何。谨行达曰渠常以为明亡于李自成。而渠则取自成之天下云。而渠意果不在于天下。则崇祯以后。当求明之遗孙以立。而吴三桂保护幼主。寄寓一隅。而与之角战。必灭乃已。所谓不取明国云者。不过假托之说也。 令曰然矣。尤庵北征之策。果是可成之事耶。谨行达曰先正之所以献议于 孝庙者。所秉执则大义也。初不以利害得失校者也。盖我国若非皇明。则已亡于壬辰。故以壬辰自处。事若不成。则当与皇明偕亡。当日君臣上下之所决定者此义也。然详观独对时所奏。则水陆并进。一遵武侯北征之策。措画亦甚密勿矣。 令曰盖是正大之义也。 孝庙以辽蓟风霜与同驱驰之意。特赐貂裘于尤庵。当日颁赐之义。至为郑重矣。闻尤庵每当 孝庙忌辰。则着此裘望哭云矣。谨行达曰 孝庙忌辰。在于暑节。而先正必着貂裘。终日痛哭于华阳深谷盘石之上。不觉声之澈天。泪之澈地。后人铭其石曰泣弓岩。 令曰千载之下。象想其深山中被裘痛哭之事。则令人零涕矣。谨行达曰 睿教极当矣。先正之苦忠如此。而不逞之徒诬先正以不忠于 孝庙。千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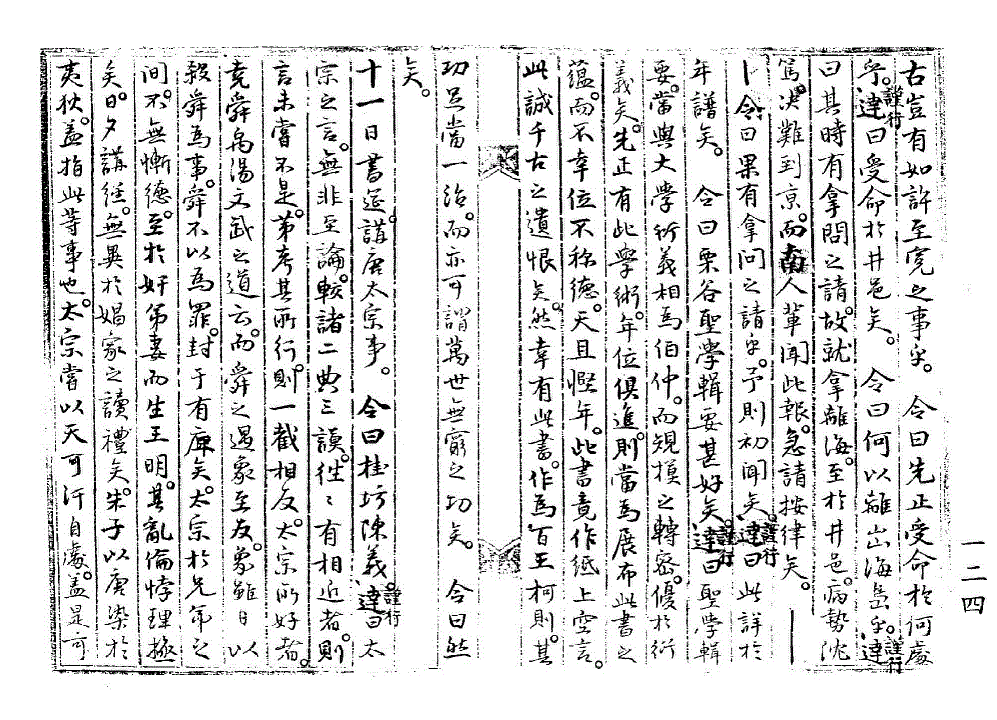 古岂有如许至冤之事乎。 令曰先正受命于何处乎。谨行达曰受命于井邑矣。 令曰何以离出海岛乎。谨行达曰其时有拿问之请。故就拿离海。至于井邑。病势沈笃。决难到京。而南人辈闻此报。急请按律矣。 令曰果有拿问之请乎。予则初闻矣。谨行达曰此详于年谱矣。 令曰栗谷圣学辑要甚好矣。谨行达曰圣学辑要。当与大学衍义相为伯仲。而规模之转密。优于衍义矣。先正有此学术。年位俱进。则当为展布此书之蕴。而不幸位不称德。天且悭年。此书竟作纸上空言。此诚千古之遗恨矣。然幸有此书。作为百王柯则。其功足当一治。而亦可谓万世无穷之功矣。 令曰然矣。
古岂有如许至冤之事乎。 令曰先正受命于何处乎。谨行达曰受命于井邑矣。 令曰何以离出海岛乎。谨行达曰其时有拿问之请。故就拿离海。至于井邑。病势沈笃。决难到京。而南人辈闻此报。急请按律矣。 令曰果有拿问之请乎。予则初闻矣。谨行达曰此详于年谱矣。 令曰栗谷圣学辑要甚好矣。谨行达曰圣学辑要。当与大学衍义相为伯仲。而规模之转密。优于衍义矣。先正有此学术。年位俱进。则当为展布此书之蕴。而不幸位不称德。天且悭年。此书竟作纸上空言。此诚千古之遗恨矣。然幸有此书。作为百王柯则。其功足当一治。而亦可谓万世无穷之功矣。 令曰然矣。十一日书筵。讲唐太宗事。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太宗之言。无非至论。较诸二典三谟。往往有相近者。则言未尝不是。第考其所行。则一截相反。太宗所好者。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云。而舜之遇象至友。象虽日以杀舜为事。舜不以为罪。封于有庳矣。太宗于兄弟之间。不无惭德。至于奸弟妻而生王明。其乱伦悖理极矣。日夕讲经。无异于娼家之读礼矣。朱子以唐染于夷狄。盖指此等事也。太宗尝以天可汗自处。盖是可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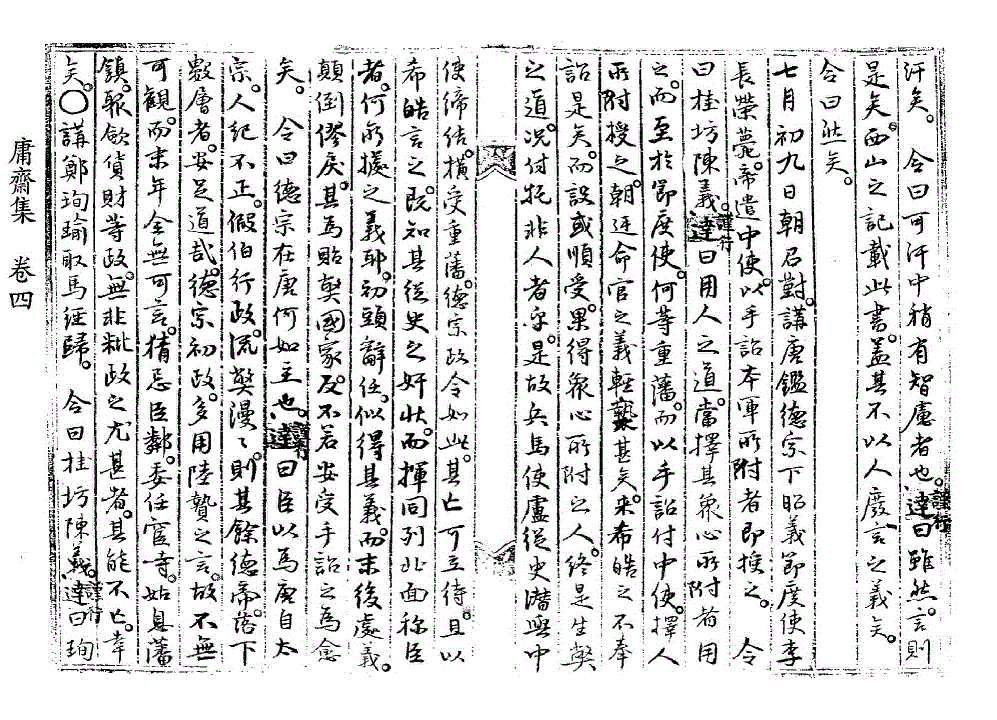 汗矣。 令曰可汗中稍有智虑者也。谨行达曰虽然。言则是矣。西山之记载此书。盖其不以人废言之义矣。 令曰然矣。
汗矣。 令曰可汗中稍有智虑者也。谨行达曰虽然。言则是矣。西山之记载此书。盖其不以人废言之义矣。 令曰然矣。七月初九日朝召对。讲唐鉴德宗下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帝遣中使。以手诏本军所附者即授之。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用人之道。当择其众心所附者用之。而至于节度使。何等重藩。而以手诏付中使。择人所附授之。朝廷命官之义轻亵甚矣。来希皓之不奉诏是矣。而设或顺受。果得众心所附之人。终是生弊之道。况付托非人者乎。是故兵马使卢从史潜与中使缔结。横受重藩。德宗政令如此。其亡可立待。且以希皓言之。既知其从史之奸状。而挥同列北面称臣者。何所据之义耶。初头辞任。似得其义。而末后处义。颠倒僇戾。其为贻弊国家。反不若安受手诏之为愈矣。 令曰德宗在唐何如主也。谨行达曰臣以为唐自太宗。人纪不正。假伯行政。流弊漫漫。则其馀德帝。落下数层者。安足道哉。德宗初政。多用陆贽之言。故不无可观。而末年全无可言。猜忌臣邻。委任宦寺。姑息藩镇。聚敛货财等政。无非秕政之尤甚者。其能不亡。幸矣。○讲郑珣瑜取马经归。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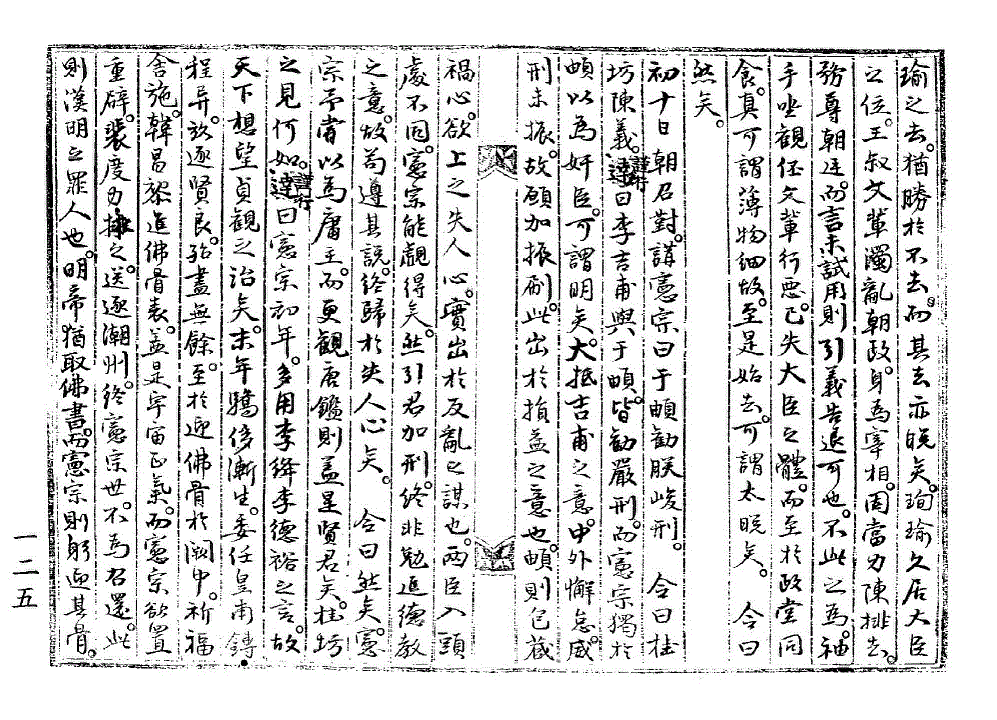 瑜之去。犹胜于不去。而其去亦晚矣。珣瑜久居大臣之位。王叔文辈浊乱朝政。身为宰相。固当力陈排去。务尊朝廷。而言未试用则引义告退可也。不此之为。袖手坐观伾文辈行恶。已失大臣之体。而至于政堂同食。真可谓薄物细故。至是始去。可谓太晚矣。 令曰然矣。
瑜之去。犹胜于不去。而其去亦晚矣。珣瑜久居大臣之位。王叔文辈浊乱朝政。身为宰相。固当力陈排去。务尊朝廷。而言未试用则引义告退可也。不此之为。袖手坐观伾文辈行恶。已失大臣之体。而至于政堂同食。真可谓薄物细故。至是始去。可谓太晚矣。 令曰然矣。初十日朝召对。讲宪宗曰于頔劝朕峻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李吉甫与于頔。皆劝严刑。而宪宗独于頔以为奸臣。可谓明矣。大抵吉甫之意。中外懈怠。威刑未振。故愿加振刷。此出于损益之意也。頔则包藏祸心。欲上之失人心。实出于反乱之谋也。两臣入头处不同。宪宗能觑得矣。然引君加刑。终非勉进德教之意。故苟遵其说。终归于失人心矣。 令曰然矣。宪宗予尝以为庸主。而更观唐鉴则盖是贤君矣。桂坊之见何如。谨行达曰宪宗初年。多用李绛李德裕之言。故天下想望贞观之治矣。末年骄侈渐生。委任皇甫镈,程异。放逐贤良。殆尽无馀。至于迎佛骨于阙中。祈福舍施。韩昌黎进佛骨表。盖是宇宙正气。而宪宗欲置重辟。裴度力救之。送逐潮州。终宪宗世。不为召还。此则汉明之罪人也。明帝犹取佛书。而宪宗则躬迎其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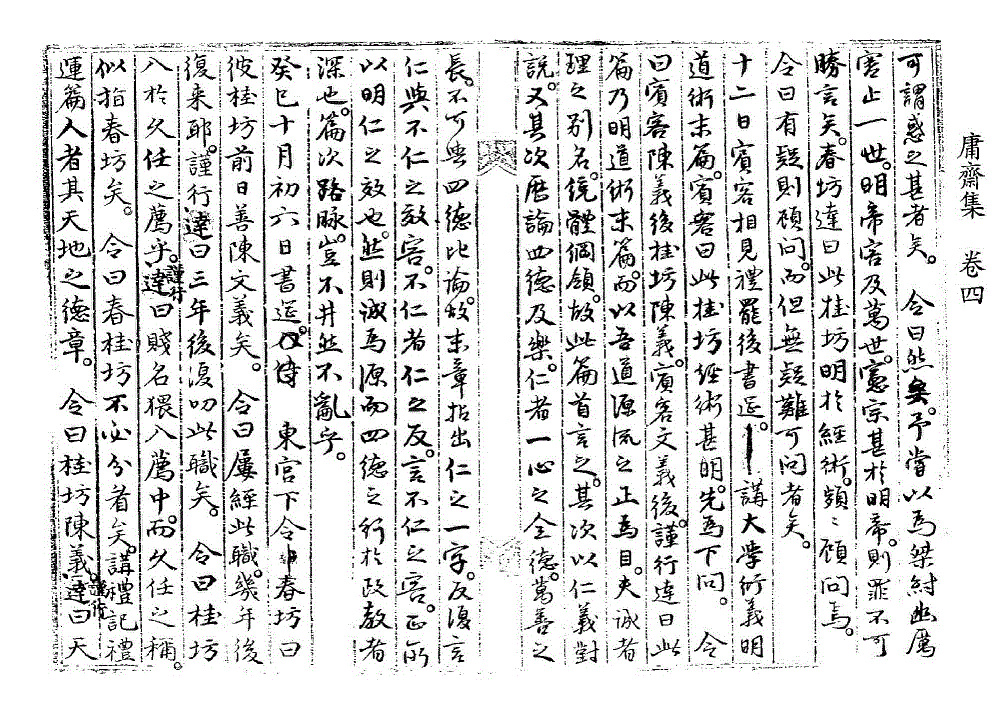 可谓惑之甚者矣。 令曰然矣。予尝以为桀纣幽厉害止一世。明帝害及万世。宪宗甚于明帝。则罪不可胜言矣。春坊达曰此桂坊明于经术。频频顾问焉。 令曰有疑则顾问。而但无疑难可问者矣。
可谓惑之甚者矣。 令曰然矣。予尝以为桀纣幽厉害止一世。明帝害及万世。宪宗甚于明帝。则罪不可胜言矣。春坊达曰此桂坊明于经术。频频顾问焉。 令曰有疑则顾问。而但无疑难可问者矣。十二日宾客相见礼罢后书筵。讲大学衍义明道术末篇。宾客曰此桂坊经术甚明。先为下问。 令曰宾客陈义后桂坊陈义。宾客文义后。谨行达曰此篇乃明道术末篇。而以吾道源流之正为目。夫诚者理之别名。统体纲领。故此篇首言之。其次以仁义对说。又其次历论四德及乐。仁者一心之全德。万善之长。不可与四德比论。故末章招出仁之一字。反复言仁与不仁之效害。不仁者仁之反。言不仁之害。正所以明仁之效也。然则诚为源而四德之行于政教者深也。篇次路脉。岂不井然不乱乎。
癸巳十月初六日书筵。 东宫下令春坊曰彼桂坊前日善陈文义矣。 令曰屡经此职。几年后复来耶。谨行达曰三年后复叨此职矣。 令曰桂坊入于久任之荐乎。谨行达曰贱名猥入荐中。而久任之称。似指春坊矣。 令曰春桂坊不必分看矣。讲礼记礼运篇人者其天地之德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天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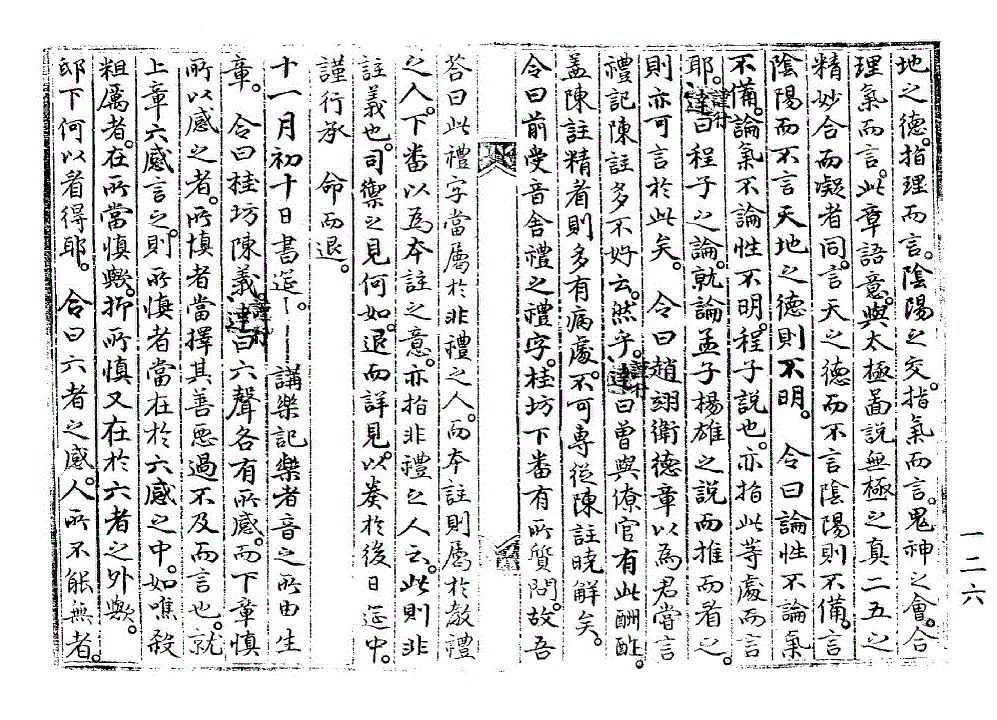 地之德。指理而言。阴阳之交。指气而言。鬼神之会。合理气而言。此章语意。与太极啚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同。言天之德而不言阴阳则不备。言阴阳而不言天地之德则不明。 令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程子说也。亦指此等处而言耶。谨行达曰程子之论。就论孟子杨雄之说而推而看之。则亦可言于此矣。 令曰赵翊卫德章以为君尝言礼记陈注多不好云。然乎。谨行达曰曾与僚官有此酬酢。盖陈注精看则多有病处。不可专从陈注晓解矣。 令曰前受音舍礼之礼字。桂坊下番有所质问。故吾答曰此礼字当属于非礼之人。而本注则属于教礼之人。下番以为本注之意。亦指非礼之人云。此则非注义也。司御之见何如。退而详见。以奏于后日筵中。谨行承 命而退。
地之德。指理而言。阴阳之交。指气而言。鬼神之会。合理气而言。此章语意。与太极啚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同。言天之德而不言阴阳则不备。言阴阳而不言天地之德则不明。 令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程子说也。亦指此等处而言耶。谨行达曰程子之论。就论孟子杨雄之说而推而看之。则亦可言于此矣。 令曰赵翊卫德章以为君尝言礼记陈注多不好云。然乎。谨行达曰曾与僚官有此酬酢。盖陈注精看则多有病处。不可专从陈注晓解矣。 令曰前受音舍礼之礼字。桂坊下番有所质问。故吾答曰此礼字当属于非礼之人。而本注则属于教礼之人。下番以为本注之意。亦指非礼之人云。此则非注义也。司御之见何如。退而详见。以奏于后日筵中。谨行承 命而退。十一月初十日书筵。讲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六声各有所感。而下章慎所以感之者。所慎者当择其善恶过不及而言也。就上章六感言之。则所慎者当在于六感之中。如噍杀粗厉者。在所当慎欤。抑所慎又在于六者之外欤。 邸下何以看得耶。 令曰六者之感。人所不能无者。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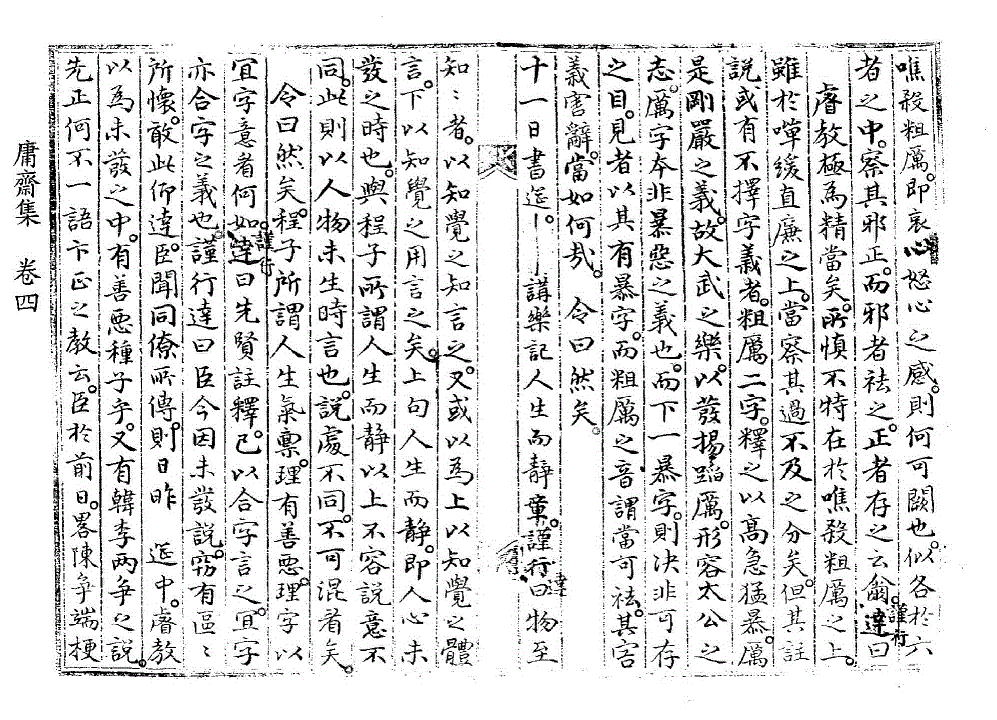 噍杀粗厉。即哀心怒心之感。则何可阙也。似各于六者之中。察其邪正。而邪者祛之。正者存之云尔。谨行达曰 睿教极为精当矣。所慎不特在于噍杀粗厉之上。虽于啴缓直廉之上。当察其过不及之分矣。但其注说或有不择字义者。粗厉二字。释之以高急猛暴。厉是刚严之义。故大武之乐。以发扬蹈厉。形容太公之志。厉字本非暴恶之义也。而下一暴字。则决非可存之目。见者以其有暴字。而粗厉之音谓当可祛。其害义害辞。当如何哉。 令曰然矣。
噍杀粗厉。即哀心怒心之感。则何可阙也。似各于六者之中。察其邪正。而邪者祛之。正者存之云尔。谨行达曰 睿教极为精当矣。所慎不特在于噍杀粗厉之上。虽于啴缓直廉之上。当察其过不及之分矣。但其注说或有不择字义者。粗厉二字。释之以高急猛暴。厉是刚严之义。故大武之乐。以发扬蹈厉。形容太公之志。厉字本非暴恶之义也。而下一暴字。则决非可存之目。见者以其有暴字。而粗厉之音谓当可祛。其害义害辞。当如何哉。 令曰然矣。十一日书筵。讲乐记人生而静章。谨行达曰物至知知者。以知觉之知言之。又或以为上以知觉之体言。下以知觉之用言之矣。上句人生而静。即人心未发之时也。与程子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意不同。此则以人物未生时言也。说处不同。不可混看矣。 令曰然矣。程子所谓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理字以宜字意看何如。谨行达曰先贤注释。已以合字言之。宜字亦合字之义也。谨行达曰臣今因未发说。窃有区区所怀。敢此仰达。臣闻同僚所传。则日昨 筵中。睿教以为未发之中。有善恶种子乎。又有韩李两争之说。先正何不一语卞正之教云。臣于前日。略陈争端梗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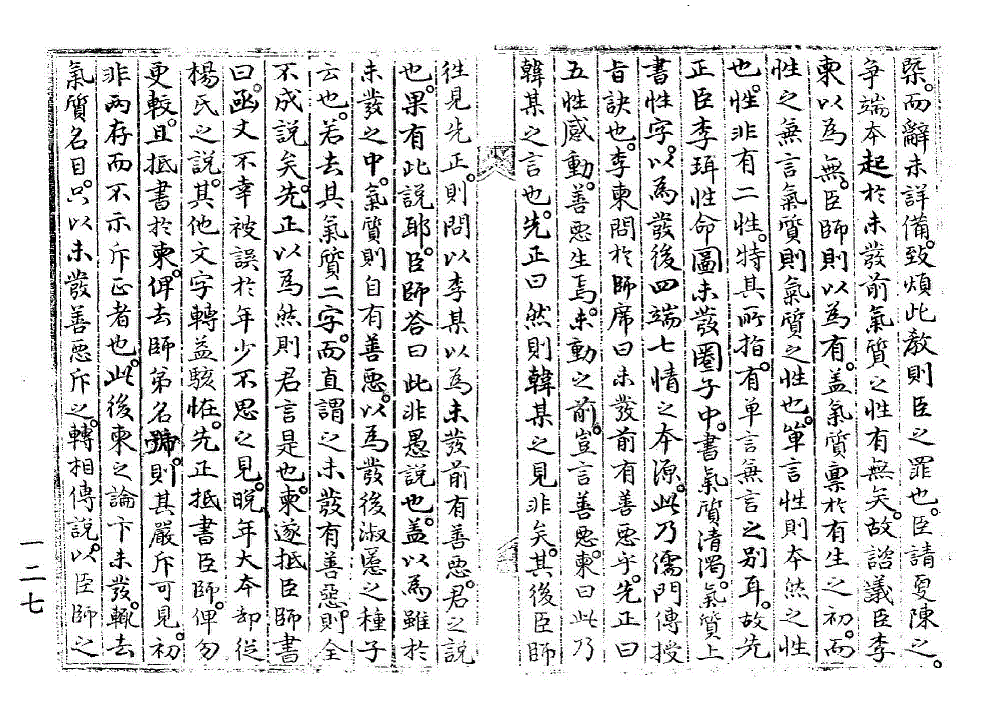 槩。而辞未详备。致烦此教则臣之罪也。臣请更陈之。争端本起于未发前气质之性有无矣。故咨议臣李柬以为无。臣师则以为有。盖气质禀于有生之初。而性之兼言气质则气质之性也。单言性则本然之性也。性非有二性。特其所指。有单言兼言之别耳。故先正臣李珥性命图未发圈子中。书气质清浊。气质上书性字。以为发后四端七情之本源。此乃儒门传授旨诀也。李柬问于师席曰未发前有善恶乎。先正曰五性感动。善恶生焉。未动之前。岂言善恶。柬曰此乃韩某之言也。先正曰然则韩某之见非矣。其后臣师往见先正。则问以李某以为未发前有善恶。君之说也。果有此说耶。臣师答曰此非愚说也。盖以为虽于未发之中。气质则自有善恶。以为发后淑慝之种子云也。若去其气质二字。而直谓之未发有善恶。则全不成说矣。先正以为然则君言是也。柬遂抵臣师书曰。函丈不幸被误于年少不思之见。晚年大本却从杨氏之说。其他文字转益骇怪。先正抵书臣师。俾勿更较。且抵书于柬。俾去师弟名号。则其严斥可见。初非两存而不示斥正者也。此后柬之论卞未发。辄去气质名目。只以未发善恶斥之。转相传说。以臣师之
槩。而辞未详备。致烦此教则臣之罪也。臣请更陈之。争端本起于未发前气质之性有无矣。故咨议臣李柬以为无。臣师则以为有。盖气质禀于有生之初。而性之兼言气质则气质之性也。单言性则本然之性也。性非有二性。特其所指。有单言兼言之别耳。故先正臣李珥性命图未发圈子中。书气质清浊。气质上书性字。以为发后四端七情之本源。此乃儒门传授旨诀也。李柬问于师席曰未发前有善恶乎。先正曰五性感动。善恶生焉。未动之前。岂言善恶。柬曰此乃韩某之言也。先正曰然则韩某之见非矣。其后臣师往见先正。则问以李某以为未发前有善恶。君之说也。果有此说耶。臣师答曰此非愚说也。盖以为虽于未发之中。气质则自有善恶。以为发后淑慝之种子云也。若去其气质二字。而直谓之未发有善恶。则全不成说矣。先正以为然则君言是也。柬遂抵臣师书曰。函丈不幸被误于年少不思之见。晚年大本却从杨氏之说。其他文字转益骇怪。先正抵书臣师。俾勿更较。且抵书于柬。俾去师弟名号。则其严斥可见。初非两存而不示斥正者也。此后柬之论卞未发。辄去气质名目。只以未发善恶斥之。转相传说。以臣师之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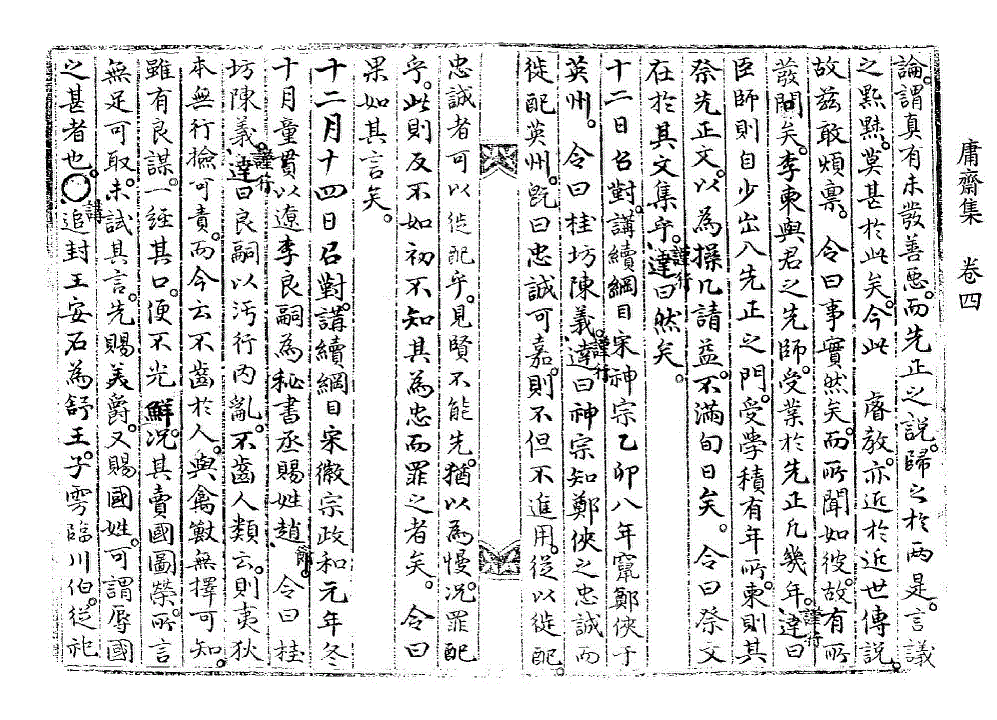 论。谓真有未发善恶。而先正之说。师之于两是。言议之䵝䵢。莫甚于此矣。今此 睿教。亦近于近世传说。故玆敢烦禀。 令曰事实然矣。而所闻如彼。故有所发问矣。李柬与君之先师。受业于先正凡几年。谨行达曰臣师则自少出入先正之门。受学积有年所。柬则其祭先正文。以为操几请益。不满旬日矣。 令曰祭文在于其文集乎。谨行达曰然矣。
论。谓真有未发善恶。而先正之说。师之于两是。言议之䵝䵢。莫甚于此矣。今此 睿教。亦近于近世传说。故玆敢烦禀。 令曰事实然矣。而所闻如彼。故有所发问矣。李柬与君之先师。受业于先正凡几年。谨行达曰臣师则自少出入先正之门。受学积有年所。柬则其祭先正文。以为操几请益。不满旬日矣。 令曰祭文在于其文集乎。谨行达曰然矣。十二日召对。讲续纲目宋神宗乙卯八年窜郑侠于英州。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神宗知郑侠之忠诚而徙配英州。既曰忠诚可嘉。则不但不进用。从以徙配。忠诚者可以徙配乎。见贤不能先。犹以为慢。况罪配乎。此则反不如初不知其为忠而罪之者矣。 令曰果如其言矣。
十二月十四日召对。讲续纲目宋徽宗政和元年冬十月童贯以辽李良嗣为秘书丞赐姓赵节。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良嗣以污行内乱。不齿人类云。则夷狄本无行捡可责。而今云不齿于人。与禽兽无择可知。虽有良谋。一经其口。便不光鲜。况其卖国图荣。所言无足可取。未试其言。先赐美爵。又赐国姓。可谓辱国之甚者也。○讲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临川伯。从祀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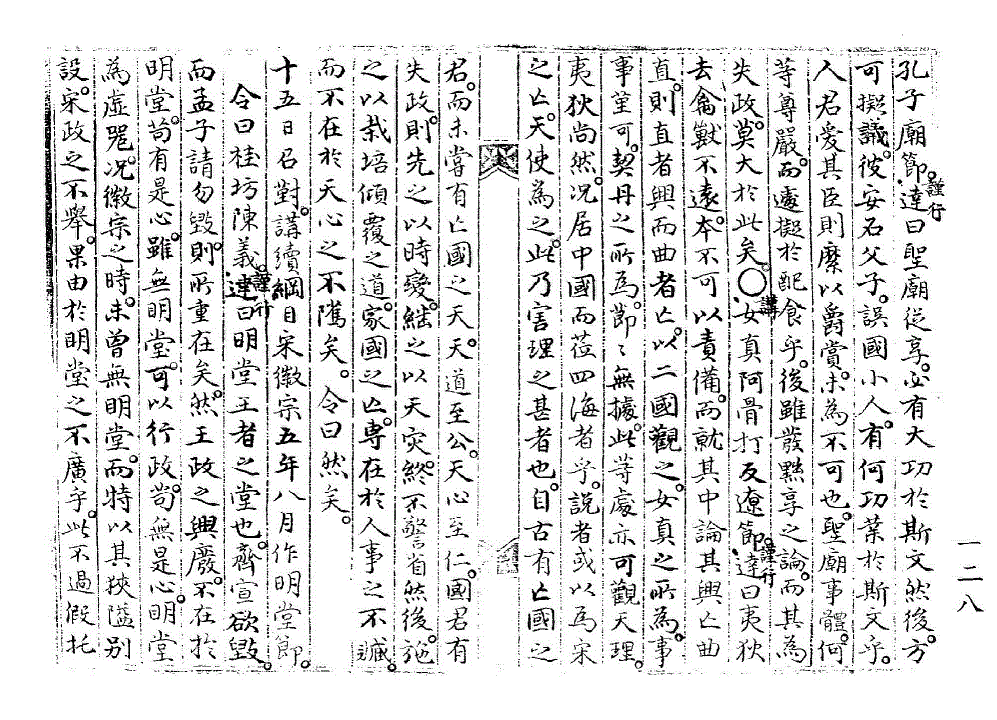 孔子庙节。谨行达曰圣庙从享。必有大功于斯文然后。方可拟议。彼安石父子。误国小人。有何功业于斯文乎。人君爱其臣则縻以爵赏。未为不可也。圣庙事体。何等尊严。而遽拟于配食乎。后虽发黜享之论。而其为失政。莫大于此矣。○讲女真阿骨打反辽节。谨行达曰夷狄去禽兽不远。本不可以责备。而就其中论其兴亡曲直。则直者兴而曲者亡。以二国观之。女真之所为。事事堇可。契丹之所为。节节无据。此等处亦可观天理。夷狄尚然。况居中国而莅四海者乎。说者或以为宋之亡。天使为之。此乃害理之甚者也。自古有亡国之君。而未尝有亡国之天。天道至公。天心至仁。国君有失政。则先之以时变。继之以天灾。终不警省然后。施之以栽培倾覆之道。家国之亡。专在于人事之不臧。而不在于天心之不骘矣。 令曰然矣。
孔子庙节。谨行达曰圣庙从享。必有大功于斯文然后。方可拟议。彼安石父子。误国小人。有何功业于斯文乎。人君爱其臣则縻以爵赏。未为不可也。圣庙事体。何等尊严。而遽拟于配食乎。后虽发黜享之论。而其为失政。莫大于此矣。○讲女真阿骨打反辽节。谨行达曰夷狄去禽兽不远。本不可以责备。而就其中论其兴亡曲直。则直者兴而曲者亡。以二国观之。女真之所为。事事堇可。契丹之所为。节节无据。此等处亦可观天理。夷狄尚然。况居中国而莅四海者乎。说者或以为宋之亡。天使为之。此乃害理之甚者也。自古有亡国之君。而未尝有亡国之天。天道至公。天心至仁。国君有失政。则先之以时变。继之以天灾。终不警省然后。施之以栽培倾覆之道。家国之亡。专在于人事之不臧。而不在于天心之不骘矣。 令曰然矣。十五日召对。讲续纲目宋徽宗五年八月作明堂节。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明堂王者之堂也。齐宣欲毁。而孟子请勿毁。则所重在矣。然王政之兴废。不在于明堂。苟有是心。虽无明堂。可以行政。苟无是心。明堂为虚器。况徽宗之时。未曾无明堂。而特以其狭隘别设。宋政之不举。果由于明堂之不广乎。此不过假托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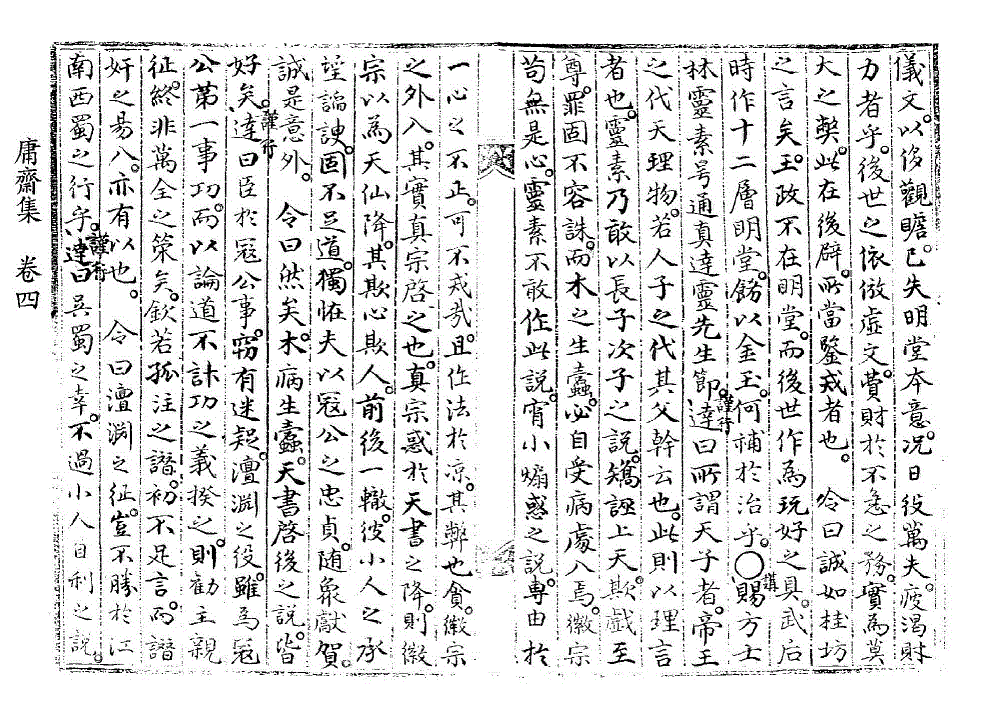 仪文。以侈观瞻。已失明堂本意。况日役万夫。疲渴财力者乎。后世之依仿虚文。费财于不急之务。实为莫大之弊。此在后辟。所当鉴戒者也。 令曰诚如桂坊之言矣。王政不在明堂。而后世作为玩好之具。武后时作十二层明堂。饬以金玉。何补于治乎。○讲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节。谨行达曰所谓天子者。帝王之代天理物。若人子之代其父干云也。此则以理言者也。灵素乃敢以长子次子之说。矫诬上天。欺戏至尊。罪固不容诛。而木之生蠹。必自受病处入焉。徽宗苟无是心。灵素不敢作此说。宵小煽惑之说。专由于一心之不正。可不戒哉。且作法于凉。其弊也贪。徽宗之外入。其实真宗启之也。真宗惑于天书之降。则徽宗以为天仙降。其欺心欺人。前后一辙。彼小人之承望谄谀。固不足道。独怪夫以寇公之忠贞。随众献贺。诚是意外。 令曰然矣。木病生蠹。天书启后之说。皆好矣。谨行达曰臣于寇公事。窃有迷疑。澶渊之役。虽为寇公第一事功。而以论道不计功之义揆之。则劝主亲征。终非万全之策矣。钦若孤注之谮。初不足言。而谮奸之易入。亦有以也。 令曰澶渊之征。岂不胜于江南西蜀之行乎。谨行达曰吴蜀之幸。不过小人自利之说。
仪文。以侈观瞻。已失明堂本意。况日役万夫。疲渴财力者乎。后世之依仿虚文。费财于不急之务。实为莫大之弊。此在后辟。所当鉴戒者也。 令曰诚如桂坊之言矣。王政不在明堂。而后世作为玩好之具。武后时作十二层明堂。饬以金玉。何补于治乎。○讲赐方士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节。谨行达曰所谓天子者。帝王之代天理物。若人子之代其父干云也。此则以理言者也。灵素乃敢以长子次子之说。矫诬上天。欺戏至尊。罪固不容诛。而木之生蠹。必自受病处入焉。徽宗苟无是心。灵素不敢作此说。宵小煽惑之说。专由于一心之不正。可不戒哉。且作法于凉。其弊也贪。徽宗之外入。其实真宗启之也。真宗惑于天书之降。则徽宗以为天仙降。其欺心欺人。前后一辙。彼小人之承望谄谀。固不足道。独怪夫以寇公之忠贞。随众献贺。诚是意外。 令曰然矣。木病生蠹。天书启后之说。皆好矣。谨行达曰臣于寇公事。窃有迷疑。澶渊之役。虽为寇公第一事功。而以论道不计功之义揆之。则劝主亲征。终非万全之策矣。钦若孤注之谮。初不足言。而谮奸之易入。亦有以也。 令曰澶渊之征。岂不胜于江南西蜀之行乎。谨行达曰吴蜀之幸。不过小人自利之说。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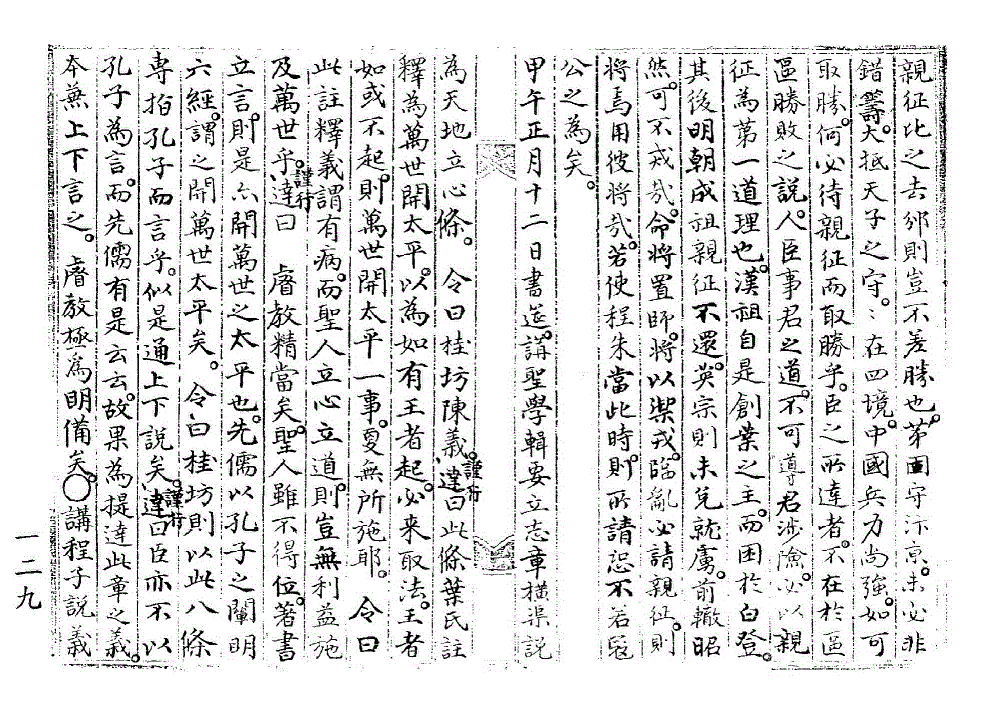 亲征比之去邠则岂不差胜也。第固守汴京。未必非错筹。大抵天子之守。守在四境。中国兵力尚强。如可取胜。何必待亲征而取胜乎。臣之所达者。不在于区区胜败之说。人臣事君之道。不可导君涉险。必以亲征为第一道理也。汉祖自是创业之主。而困于白登。其后明朝成祖亲征不还。英宗则未免就虏。前辙昭然。可不戒哉。命将置师。将以御戎。临乱必请亲征。则将焉用彼将哉。若使程朱当此时。则所请恐不若寇公之为矣。
亲征比之去邠则岂不差胜也。第固守汴京。未必非错筹。大抵天子之守。守在四境。中国兵力尚强。如可取胜。何必待亲征而取胜乎。臣之所达者。不在于区区胜败之说。人臣事君之道。不可导君涉险。必以亲征为第一道理也。汉祖自是创业之主。而困于白登。其后明朝成祖亲征不还。英宗则未免就虏。前辙昭然。可不戒哉。命将置师。将以御戎。临乱必请亲征。则将焉用彼将哉。若使程朱当此时。则所请恐不若寇公之为矣。甲午正月十二日书筵。讲圣学辑要立志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此条叶氏注释为万世开太平。以为如有王者起。必来取法。王者如或不起。则万世开太平一事。更无所施耶。 令曰此注释义谓有病。而圣人立心立道。则岂无利益施及万世乎。谨行达曰 睿教精当矣。圣人虽不得位。著书立言。则是亦开万世之太平也。先儒以孔子之阐明六经。谓之开万世太平矣。 令曰桂坊则以此八条专指孔子而言乎。似是通上下说矣。谨行达曰臣亦不以孔子为言。而先儒有是云云。故果为提达此章之义。本兼上下言之。 睿教极为明备矣。○讲程子说义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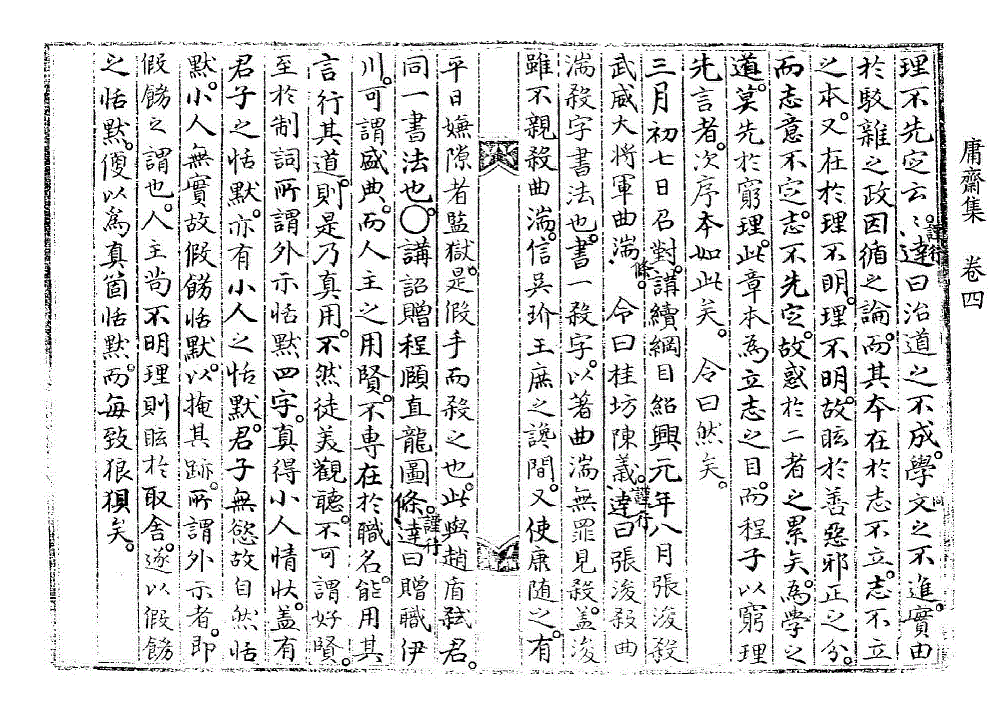 理不先定云云。谨行达曰治道之不成。学问之不进。实由于驳杂之政因循之论。而其本在于志不立。志不立之本。又在于理不明。理不明。故眩于善恶邪正之分。而志意不定。志不先定。故惑于二者之累矣。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此章本为立志之目。而程子以穷理先言者。次序本如此矣。 令曰然矣。
理不先定云云。谨行达曰治道之不成。学问之不进。实由于驳杂之政因循之论。而其本在于志不立。志不立之本。又在于理不明。理不明。故眩于善恶邪正之分。而志意不定。志不先定。故惑于二者之累矣。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此章本为立志之目。而程子以穷理先言者。次序本如此矣。 令曰然矣。三月初七日召对。讲续纲目绍兴元年八月张浚杀武威大将军曲湍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张浚杀曲湍杀字书法也。书一杀字。以著曲湍无罪见杀。盖浚虽不亲杀曲湍。信吴玠王庶之谗间。又使康随之。有平日嫌隙者监狱。是假手而杀之也。此与赵盾弑君。同一书法也。○讲诏赠程颐直龙图条。谨行达曰赠职伊川。可谓盛典。而人主之用贤。不专在于职名。能用其言行其道。则是乃真用。不然徒美观听。不可谓好贤。至于制词所谓外示恬默四字。真得小人情状。盖有君子之恬默。亦有小人之恬默。君子无欲故自然恬默。小人无实故假饬恬默。以掩其迹。所谓外示者。即假饬之谓也。人主苟不明理则眩于取舍。遂以假饬之恬默。便以为真个恬默。而每致狼狈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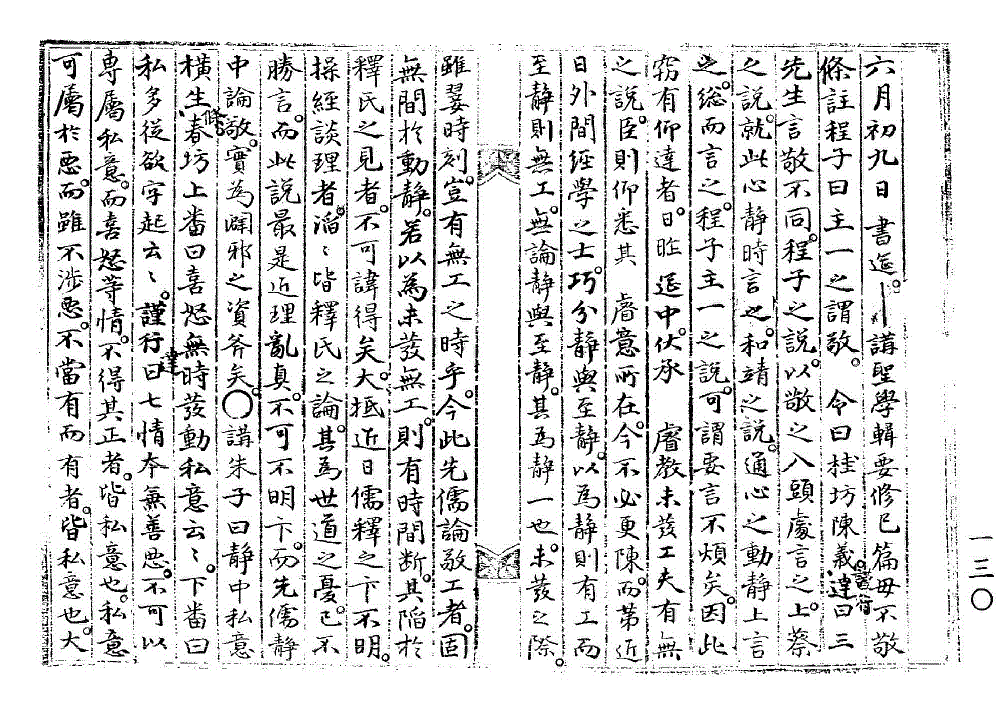 六月初九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修己篇毋不敬条注程子曰主一之谓敬。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三先生言敬不同。程子之说。以敬之入头处言之。上蔡之说。就此心静时言之。和靖之说。通心之动静上言之。总而言之。程子主一之说。可谓要言不烦矣。因此窃有仰达者。日昨筵中。伏承 睿教未发工夫有无之说。臣则仰悉其 睿意所在。今不必更陈。而第近日外间经学之士。巧分静与至静。以为静则有工而至静则无工。无论静与至静。其为静一也。未发之际。虽翣时刻。岂有无工之时乎。今此先儒论敬工者。固无间于动静。若以为未发无工。则有时间断。其陷于释氏之见者。不可讳得矣。大抵近日儒释之卞不明。操经谈理者。滔滔皆释氏之论。其为世道之忧。已不胜言。而此说最是近理乱真。不可不明卞。而先儒静中论敬。实为辟邪之资斧矣。○讲朱子曰静中私意横生条。春坊上番曰喜怒无时发动私意云云。下番曰私多从欲字起云云。谨行达曰七情本兼善恶。不可以专属私意。而喜怒等情。不得其正者。皆私意也。私意可属于恶。而虽不涉恶。不当有而有者。皆私意也。大
六月初九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修己篇毋不敬条注程子曰主一之谓敬。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三先生言敬不同。程子之说。以敬之入头处言之。上蔡之说。就此心静时言之。和靖之说。通心之动静上言之。总而言之。程子主一之说。可谓要言不烦矣。因此窃有仰达者。日昨筵中。伏承 睿教未发工夫有无之说。臣则仰悉其 睿意所在。今不必更陈。而第近日外间经学之士。巧分静与至静。以为静则有工而至静则无工。无论静与至静。其为静一也。未发之际。虽翣时刻。岂有无工之时乎。今此先儒论敬工者。固无间于动静。若以为未发无工。则有时间断。其陷于释氏之见者。不可讳得矣。大抵近日儒释之卞不明。操经谈理者。滔滔皆释氏之论。其为世道之忧。已不胜言。而此说最是近理乱真。不可不明卞。而先儒静中论敬。实为辟邪之资斧矣。○讲朱子曰静中私意横生条。春坊上番曰喜怒无时发动私意云云。下番曰私多从欲字起云云。谨行达曰七情本兼善恶。不可以专属私意。而喜怒等情。不得其正者。皆私意也。私意可属于恶。而虽不涉恶。不当有而有者。皆私意也。大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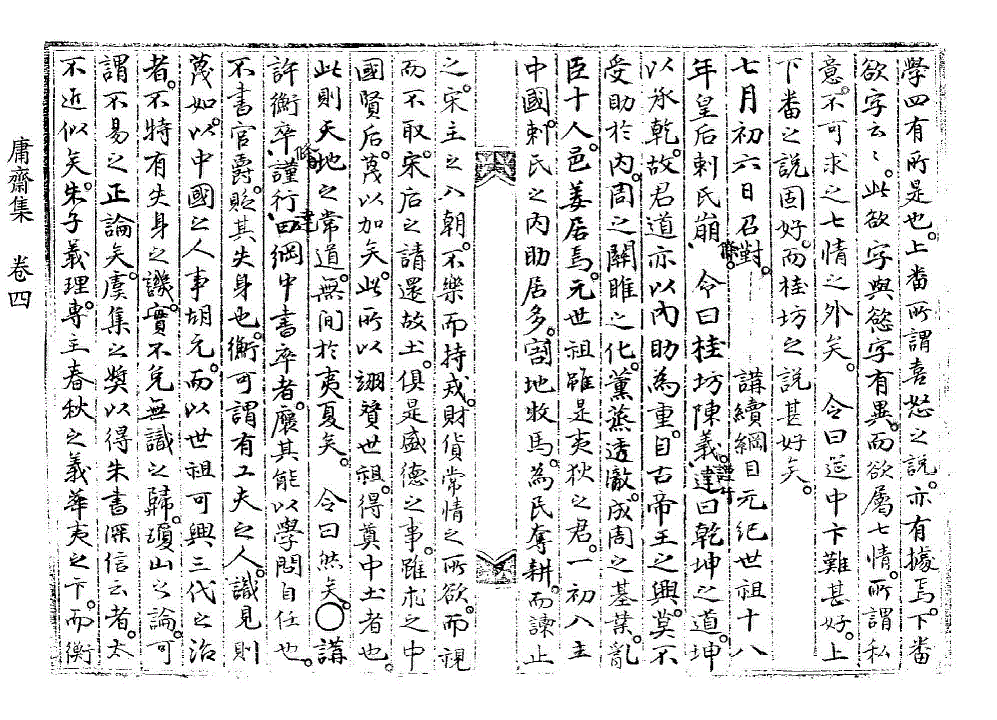 学四有所是也。上番所谓喜怒之说。亦有据焉。下番欲字云云。此欲字与欲字有异。而欲属七情。所谓私意。不可求之七情之外矣。 令曰筵中卞难甚好。上下番之说固好。而桂坊之说甚好矣。
学四有所是也。上番所谓喜怒之说。亦有据焉。下番欲字云云。此欲字与欲字有异。而欲属七情。所谓私意。不可求之七情之外矣。 令曰筵中卞难甚好。上下番之说固好。而桂坊之说甚好矣。七月初六日召对。讲续纲目元纪世祖十八年皇后剌氏崩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乾坤之道。坤以承乾。故君道亦以内助为重。自古帝王之兴。莫不受助于内。周之关雎之化。薰蒸透澈。成周之基业。乱臣十人。邑姜居焉。元世祖虽是夷狄之君。一初入主中国。剌氏之内助居多。割地牧马。为民夺耕。而谏止之。宋主之入朝。不乐而持戒。财货常情之所欲。而视而不取。宋后之请还故土。俱是盛德之事。虽求之中国贤后。蔑以加矣。此所以翊赞世祖。得奠中土者也。此则天地之常道。无间于夷夏矣。 令曰然矣。○讲许衡卒条。谨行达曰纲中书卒者。褒其能以学问自任也。不书官爵。贬其失身也。衡可谓有工夫之人。识见则蔑如。以中国之人事胡元。而以世祖可兴三代之治者。不特有失身之讥。实不免无识之归。琼山之论。可谓不易之正论矣。虞集之奖以得朱书深信云者。太不近似矣。朱子义理。专主春秋之义华夷之卞。而衡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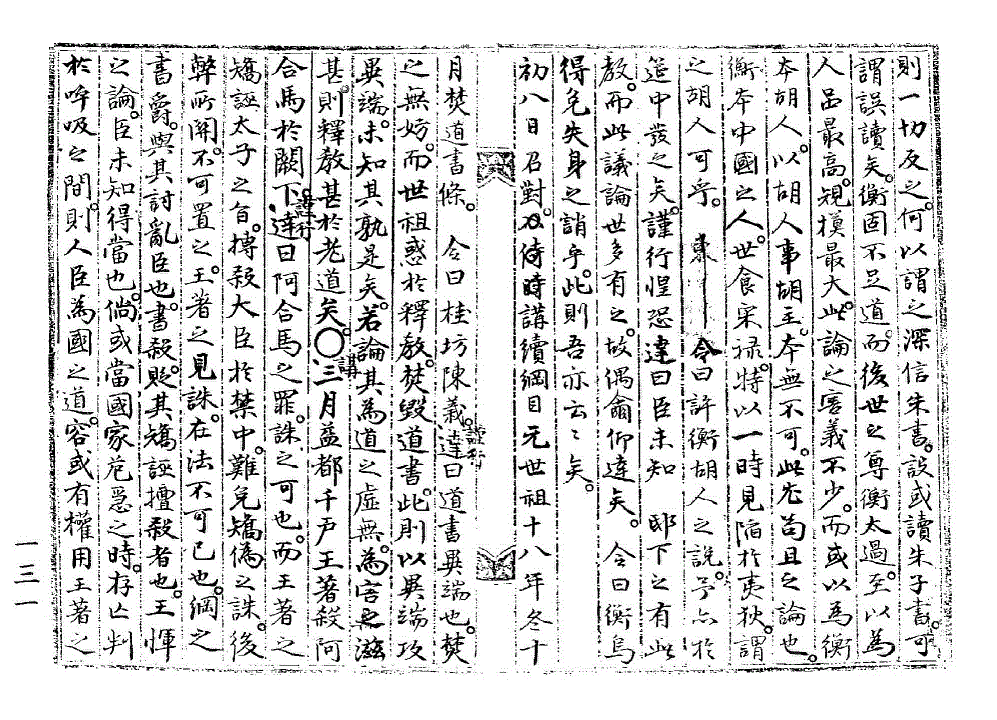 则一切反之。何以谓之深信朱书。设或读朱子书。可谓误读矣。衡固不足道。而后世之尊衡太过。至以为人品最高。规模最大。此论之害义不少。而或以为衡本胡人。以胡人事胡主。本无不可。此尤苟且之论也。衡本中国之人。世食宋禄。特以一时见陷于夷狄。谓之胡人可乎。 令曰许衡胡人之说。予亦于筵中发之矣。谨行惶恐达曰臣未知 邸下之有此教。而此议论世多有之。故偶尔仰达矣。 令曰衡乌得免失身之诮乎。此则吾亦云云矣。
则一切反之。何以谓之深信朱书。设或读朱子书。可谓误读矣。衡固不足道。而后世之尊衡太过。至以为人品最高。规模最大。此论之害义不少。而或以为衡本胡人。以胡人事胡主。本无不可。此尤苟且之论也。衡本中国之人。世食宋禄。特以一时见陷于夷狄。谓之胡人可乎。 令曰许衡胡人之说。予亦于筵中发之矣。谨行惶恐达曰臣未知 邸下之有此教。而此议论世多有之。故偶尔仰达矣。 令曰衡乌得免失身之诮乎。此则吾亦云云矣。初八日召对。讲续纲目元世祖十八年冬十月焚道书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道书异端也。焚之无妨。而世祖惑于释教。焚毁道书。此则以异端攻异端。未知其孰是矣。若论其为道之虚无。为害之滋甚。则释教甚于老道矣。○讲三月益都千户王著杀阿合马于阙下。谨行达曰阿合马之罪。诛之可也。而王著之矫诬太子之旨。搏杀大臣于禁中。难免矫伪之诛。后弊所关。不可置之。王著之见诛。在法不可已也。纲之书爵。与其讨乱臣也。书杀。贬其矫诬擅杀者也。王恽之论。臣未知得当也。倘或当国家危急之时。存亡判于呼吸之间。则人臣为国之道。容或有权用王著之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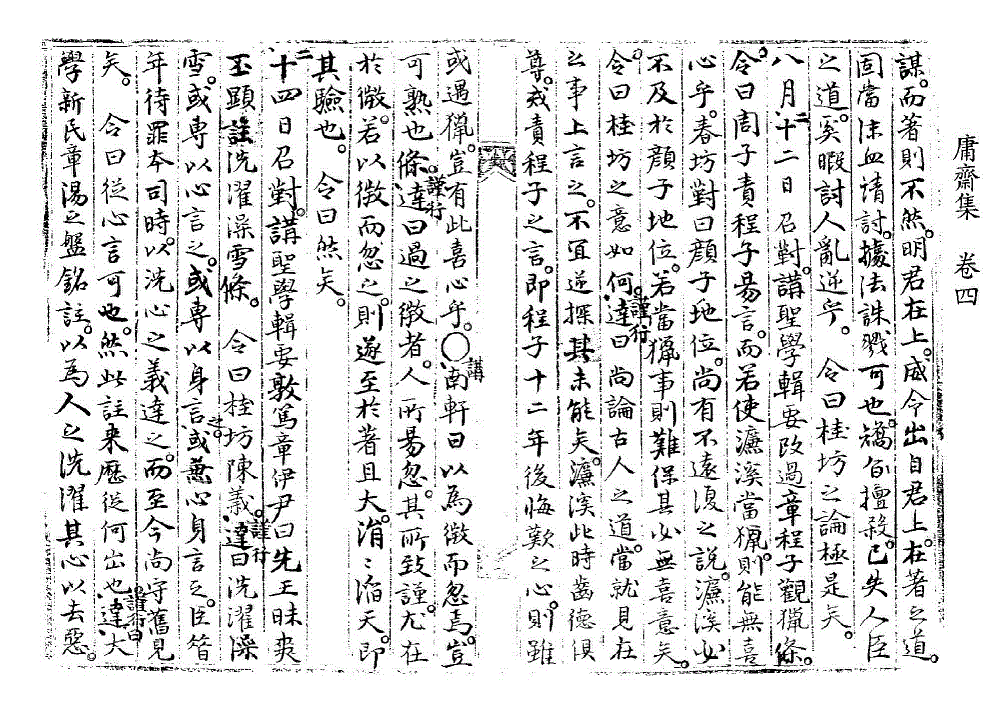 谋。而著则不然。明君在上。威令出自君上。在著之道。固当沫血请讨。据法诛戮可也。矫旨擅杀。已失人臣之道。奚暇讨人乱逆乎。 令曰桂坊之论极是矣。
谋。而著则不然。明君在上。威令出自君上。在著之道。固当沫血请讨。据法诛戮可也。矫旨擅杀。已失人臣之道。奚暇讨人乱逆乎。 令曰桂坊之论极是矣。八月二十二日召对。讲圣学辑要改过章程子观猎条。 令曰周子责程子易言。而若使濂溪当猎。则能无喜心乎。春坊对曰颜子地位。尚有不远复之说。濂溪必不及于颜子地位。若当猎事则难保其必无喜意矣。 令曰桂坊之意如何。谨行达曰尚论古人之道。当就见在之事上言之。不宜逆探其未能矣。濂溪此时齿德俱尊。戒责程子之言。即程子十二年后悔叹之心。则虽或遇猎。岂有此喜心乎。○讲南轩曰以为微而忽焉。岂可熟也条。谨行达曰过之微者。人所易忽。其所致谨。尤在于微。若以微而忽之。则遂至于著且大。涓涓滔天。即其验也。 令曰然矣。
二十四日召对。讲圣学辑要敦笃章伊尹曰先王昧爽丕显注洗濯澡雪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洗濯澡雪。或专以心言之。或专以身言之。或兼心身言之。臣昔年待罪本司时。以洗心之义达之。而至今尚守旧见矣。 令曰从心言可也。然此注来历从何出也。谨行达曰大学新民章汤之盘铭注。以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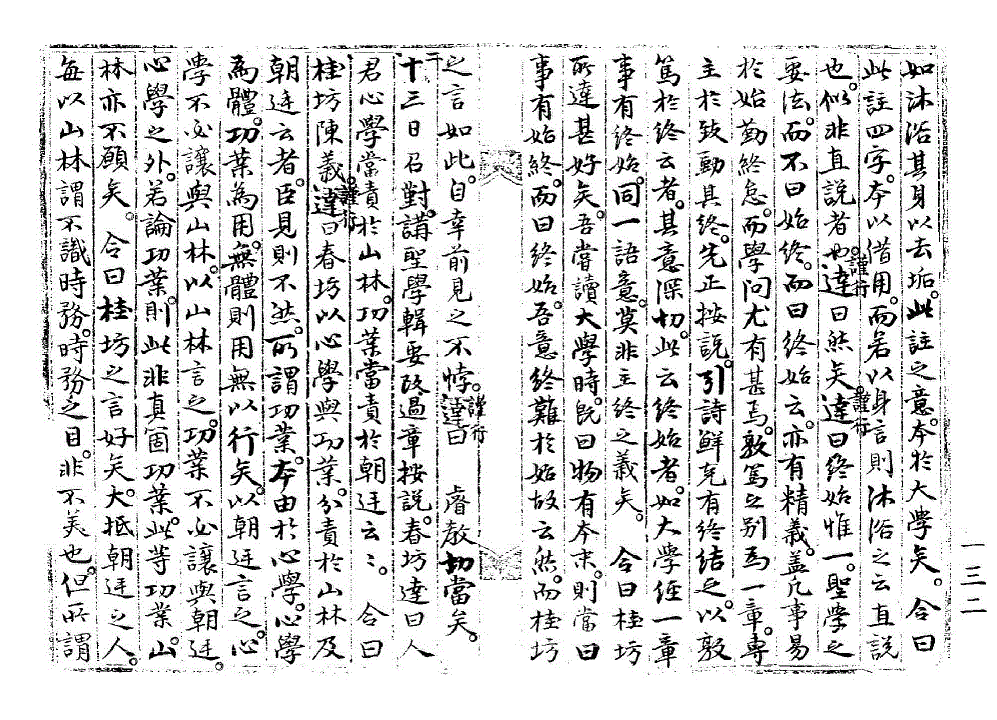 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此注之意。本于大学矣。 令曰此注四字。本以借用。而若以身言则沐浴之云直说也。似非直说者也。谨行达曰然矣。谨行达曰终始惟一。圣学之要法。而不曰始终。而曰终始云。亦有精义。盖凡事易于始勤终怠。而学问尤有甚焉。敦笃之别为一章。专主于致勤其终。先正按说。引诗鲜克有终结之。以敦笃于终云者。其意深切。此云终始者。如大学经一章事有终始。同一语意。莫非主终之义矣。 令曰桂坊所达甚好矣。吾尝读大学时。既曰物有本末。则当曰事有始终。而曰终始。吾意终难于始故云然。而桂坊之言如此。自幸前见之不悖。谨行达曰 睿教切当矣。
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此注之意。本于大学矣。 令曰此注四字。本以借用。而若以身言则沐浴之云直说也。似非直说者也。谨行达曰然矣。谨行达曰终始惟一。圣学之要法。而不曰始终。而曰终始云。亦有精义。盖凡事易于始勤终怠。而学问尤有甚焉。敦笃之别为一章。专主于致勤其终。先正按说。引诗鲜克有终结之。以敦笃于终云者。其意深切。此云终始者。如大学经一章事有终始。同一语意。莫非主终之义矣。 令曰桂坊所达甚好矣。吾尝读大学时。既曰物有本末。则当曰事有始终。而曰终始。吾意终难于始故云然。而桂坊之言如此。自幸前见之不悖。谨行达曰 睿教切当矣。二十三日召对。讲圣学辑要改过章按说。春坊达曰人君心学当责于山林。功业当责于朝廷云云。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春坊以心学与功业。分责于山林及朝廷云者。臣见则不然。所谓功业。本由于心学。心学为体。功业为用。无体则用无以行矣。以朝廷言之。心学不必让与山林。以山林言之。功业不必让与朝廷。心学之外。若论功业。则此非真个功业。此等功业。山林亦不愿矣。 令曰桂坊之言好矣。大抵朝廷之人。每以山林谓不识时务。时务之目。非不美也。但所谓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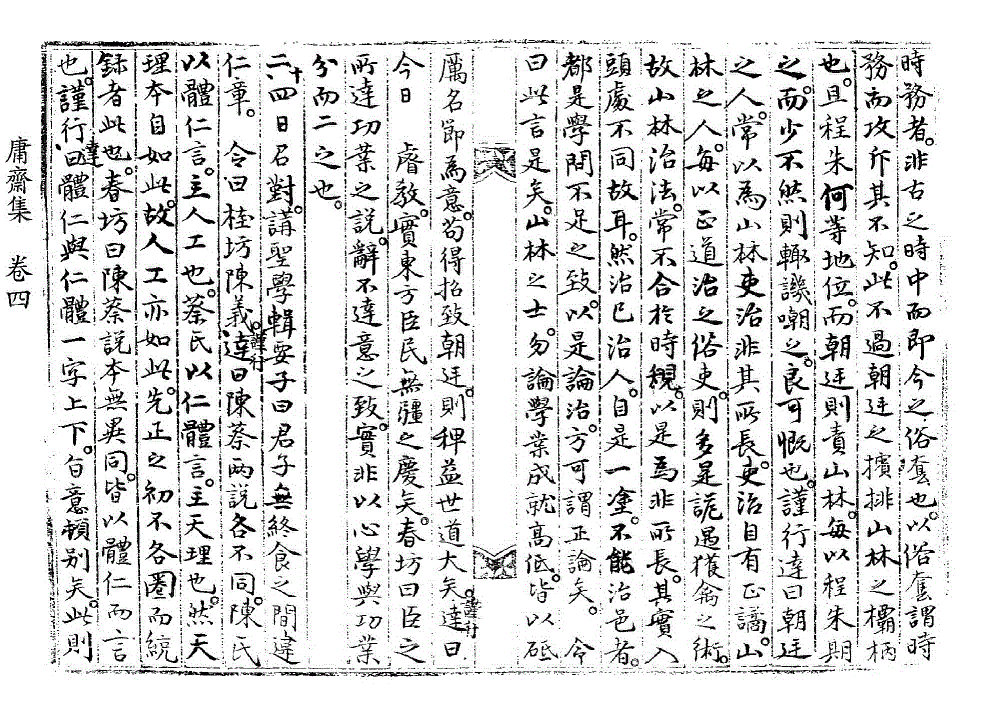 时务者。非古之时中而即今之俗套也。以俗套谓时务而攻斥其不知。此不过朝廷之摈排山林之把柄也。且程朱何等地位。而朝廷则责山林。每以程朱期之。而少不然则辄讥嘲之。良可慨也。谨行达曰朝廷之人。常以为山林吏治非其所长。吏治自有正谲。山林之人。每以正道治之俗吏。则多是诡遇获禽之术。故山林治法。常不合于时规。以是为非所长。其实入头处不同故耳。然治己治人。自是一涂。不能治邑者。都是学问不足之致。以是论治。方可谓正论矣。 令曰此言是矣。山林之士。勿论学业成就高低。皆以砥厉名节为意。苟得招致朝廷。则稗益世道大矣。谨行达曰今日 睿教。实东方臣民无疆之庆矣。春坊曰臣之所达功业之说。辞不达意之致。实非以心学与功业分而二之也。
时务者。非古之时中而即今之俗套也。以俗套谓时务而攻斥其不知。此不过朝廷之摈排山林之把柄也。且程朱何等地位。而朝廷则责山林。每以程朱期之。而少不然则辄讥嘲之。良可慨也。谨行达曰朝廷之人。常以为山林吏治非其所长。吏治自有正谲。山林之人。每以正道治之俗吏。则多是诡遇获禽之术。故山林治法。常不合于时规。以是为非所长。其实入头处不同故耳。然治己治人。自是一涂。不能治邑者。都是学问不足之致。以是论治。方可谓正论矣。 令曰此言是矣。山林之士。勿论学业成就高低。皆以砥厉名节为意。苟得招致朝廷。则稗益世道大矣。谨行达曰今日 睿教。实东方臣民无疆之庆矣。春坊曰臣之所达功业之说。辞不达意之致。实非以心学与功业分而二之也。二十四日召对。讲圣学辑要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陈蔡两说各不同。陈氏以体仁言。主人工也。蔡氏以仁体言。主天理也。然天理本自如此。故人工亦如此。先正之初不各圈而统录者此也。春坊曰陈蔡说本无异同。皆以体仁而言也。谨行达曰体仁与仁体一字上下。旨意顿别矣。此则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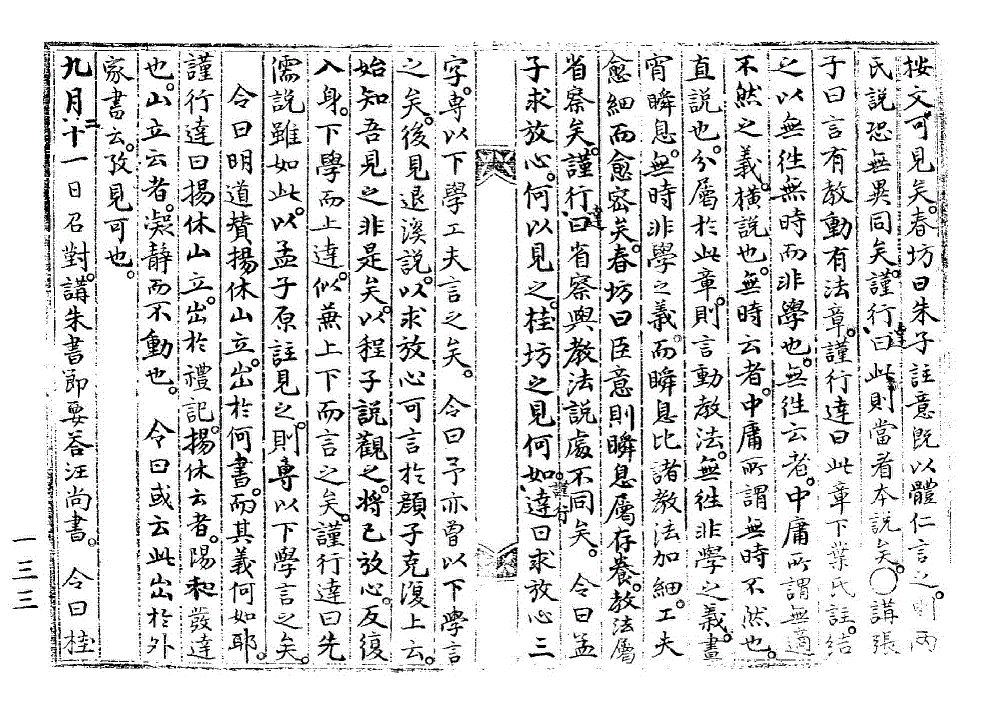 按文可见矣。春坊曰朱子注意既以体仁言之。则两氏说恐无异同矣。谨行达曰此则当看本说矣。○讲张子曰言有教动有法章。谨行达曰此章下叶氏注。结之以无往无时而非学也。无往云者。中庸所谓无适不然之义。横说也。无时云者。中庸所谓无时不然也。直说也。分属于此章。则言动教法。无往非学之义。昼宵瞬息。无时非学之义。而瞬息比诸教法加细。工夫愈细而愈密矣。春坊曰臣意则瞬息属存养。教法属省察矣。谨行达曰省察与教法说处不同矣。 令曰孟子求放心。何以见之。桂坊之见何如。谨行达曰求放心三字。专以下学工夫言之矣。 令曰予亦曾以下学言之矣。后见退溪说。以求放心可言于颜子克复上云。始知吾见之非是矣。以程子说观之。将已放心。反复入身。下学而上达。似兼上下而言之矣。谨行达曰先儒说虽如此。以孟子原注见之。则专以下学言之矣。 令曰明道赞扬休山立。出于何书。而其义何如耶。谨行达曰扬休山立。出于礼记。扬休云者。阳和发达也。山立云者。凝静而不动也。 令曰或云此出于外家书云。考见可也。
按文可见矣。春坊曰朱子注意既以体仁言之。则两氏说恐无异同矣。谨行达曰此则当看本说矣。○讲张子曰言有教动有法章。谨行达曰此章下叶氏注。结之以无往无时而非学也。无往云者。中庸所谓无适不然之义。横说也。无时云者。中庸所谓无时不然也。直说也。分属于此章。则言动教法。无往非学之义。昼宵瞬息。无时非学之义。而瞬息比诸教法加细。工夫愈细而愈密矣。春坊曰臣意则瞬息属存养。教法属省察矣。谨行达曰省察与教法说处不同矣。 令曰孟子求放心。何以见之。桂坊之见何如。谨行达曰求放心三字。专以下学工夫言之矣。 令曰予亦曾以下学言之矣。后见退溪说。以求放心可言于颜子克复上云。始知吾见之非是矣。以程子说观之。将已放心。反复入身。下学而上达。似兼上下而言之矣。谨行达曰先儒说虽如此。以孟子原注见之。则专以下学言之矣。 令曰明道赞扬休山立。出于何书。而其义何如耶。谨行达曰扬休山立。出于礼记。扬休云者。阳和发达也。山立云者。凝静而不动也。 令曰或云此出于外家书云。考见可也。九月二十一日召对。讲朱书节要答汪尚书。 令曰桂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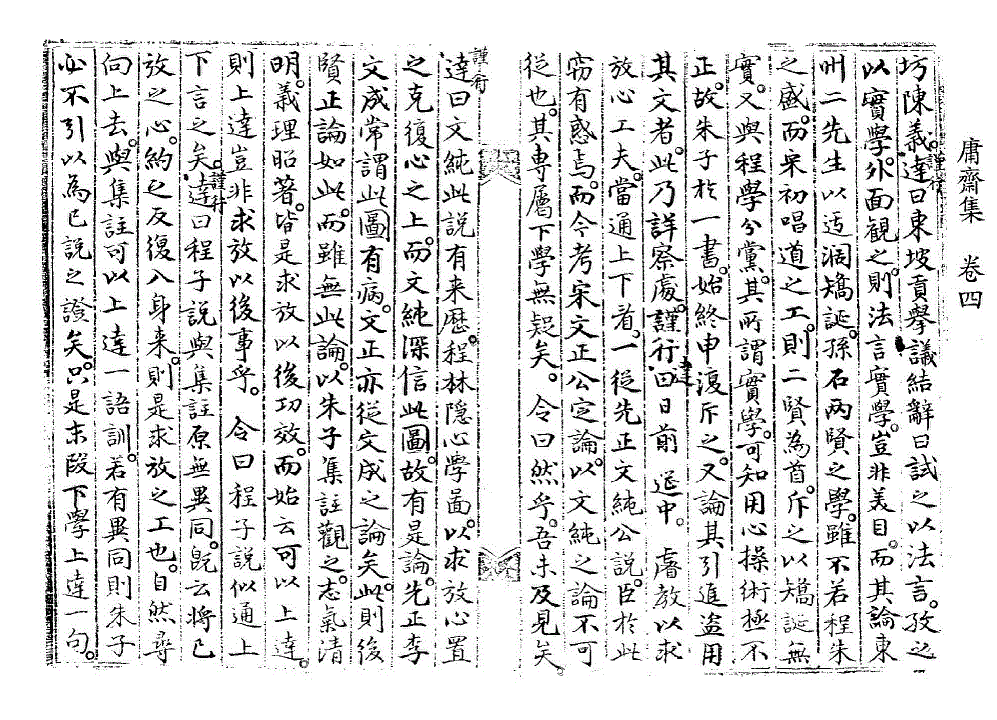 坊陈义。谨行达曰东坡贡举议结辞曰试之以法言。孜之以实学。外面观之。则法言实学。岂非美目。而其论东州二先生以迂阔矫诞。孙石两贤之学。虽不若程朱之盛。而宋初唱道之工。则二贤为首。斥之以矫诞无实。又与程学分党。其所谓实学。可知用心操术极不正。故朱子于一书。始终申复斥之。又论其引进盗用其文者。此乃详察处。谨行达曰日前 筵中。 睿教以求放心工夫。当通上下看。一从先正文纯公说。臣于此窃有惑焉。而今考宋文正公定论。以文纯之论不可从也。其专属下学无疑矣。 令曰然乎。吾未及见矣。谨行达曰文纯此说有来历。程林隐心学啚。以求放心置之克复心之上。而文纯深信此图。故有是论。先正李文成常谓此图有病。文正亦从文成之论矣。此则后贤正论如此。而虽无此论。以朱子集注观之。志气清明。义理昭著。皆是求放以后功效。而始云可以上达。则上达岂非求放以后事乎。 令曰程子说似通上下言之矣。谨行达曰程子说与集注原无异同。既云将已放之心。约之反复入身来。则是求放之工也。自然寻向上去。与集注可以上达一语训。若有异同则朱子必不引以为已说之證矣。只是末段下学上达一句。
坊陈义。谨行达曰东坡贡举议结辞曰试之以法言。孜之以实学。外面观之。则法言实学。岂非美目。而其论东州二先生以迂阔矫诞。孙石两贤之学。虽不若程朱之盛。而宋初唱道之工。则二贤为首。斥之以矫诞无实。又与程学分党。其所谓实学。可知用心操术极不正。故朱子于一书。始终申复斥之。又论其引进盗用其文者。此乃详察处。谨行达曰日前 筵中。 睿教以求放心工夫。当通上下看。一从先正文纯公说。臣于此窃有惑焉。而今考宋文正公定论。以文纯之论不可从也。其专属下学无疑矣。 令曰然乎。吾未及见矣。谨行达曰文纯此说有来历。程林隐心学啚。以求放心置之克复心之上。而文纯深信此图。故有是论。先正李文成常谓此图有病。文正亦从文成之论矣。此则后贤正论如此。而虽无此论。以朱子集注观之。志气清明。义理昭著。皆是求放以后功效。而始云可以上达。则上达岂非求放以后事乎。 令曰程子说似通上下言之矣。谨行达曰程子说与集注原无异同。既云将已放之心。约之反复入身来。则是求放之工也。自然寻向上去。与集注可以上达一语训。若有异同则朱子必不引以为已说之證矣。只是末段下学上达一句。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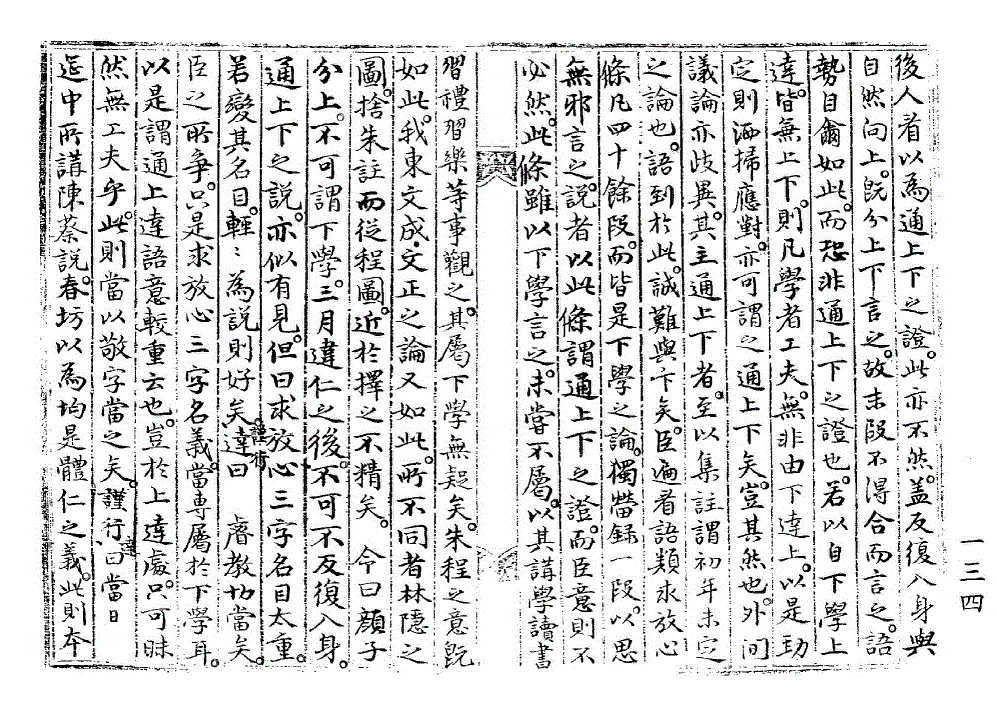 后人看以为通上下之證。此亦不然。盖反复入身与自然向上。既分上下言之。故末段不得合而言之。语势自尔如此。而恐非通上下之證也。若以自下学上达。皆兼上下。则凡学者工夫。无非由下达上。以是劲定则洒扫应对。亦可谓之通上下矣。岂其然也。外间议论亦歧异。其主通上下者。至以集注谓初年未定之论也。语到于此。诚难与卞矣。臣遍看语类求放心条凡四十馀段。而皆是下学之论。独㽦录一段。以思无邪言之。说者以此条谓通上下之證。而臣意则不必然。此条虽以下学言之。未尝不属。以其讲学读书习礼习乐等事观之。其属下学无疑矣。朱程之意既如此。我东文成,文正之论又如此。所不同者林隐之图。舍朱注而从程图。近于择之不精矣。 令曰颜子分上。不可谓下学。三月违仁之后。不可不反复入身。通上下之说。亦似有见。但曰求放心三字名目太重。若变其名目。轻轻为说则好矣。谨行达曰 睿教切当矣。臣之所争。只是求放心三字名义。当专属于下学耳。以是谓通上达语意较重云也。岂于上达处。只可昧然无工夫乎。此则当以敬字当之矣。谨行达曰当日 筵中所讲陈蔡说。春坊以为均是体仁之义。此则本
后人看以为通上下之證。此亦不然。盖反复入身与自然向上。既分上下言之。故末段不得合而言之。语势自尔如此。而恐非通上下之證也。若以自下学上达。皆兼上下。则凡学者工夫。无非由下达上。以是劲定则洒扫应对。亦可谓之通上下矣。岂其然也。外间议论亦歧异。其主通上下者。至以集注谓初年未定之论也。语到于此。诚难与卞矣。臣遍看语类求放心条凡四十馀段。而皆是下学之论。独㽦录一段。以思无邪言之。说者以此条谓通上下之證。而臣意则不必然。此条虽以下学言之。未尝不属。以其讲学读书习礼习乐等事观之。其属下学无疑矣。朱程之意既如此。我东文成,文正之论又如此。所不同者林隐之图。舍朱注而从程图。近于择之不精矣。 令曰颜子分上。不可谓下学。三月违仁之后。不可不反复入身。通上下之说。亦似有见。但曰求放心三字名目太重。若变其名目。轻轻为说则好矣。谨行达曰 睿教切当矣。臣之所争。只是求放心三字名义。当专属于下学耳。以是谓通上达语意较重云也。岂于上达处。只可昧然无工夫乎。此则当以敬字当之矣。谨行达曰当日 筵中所讲陈蔡说。春坊以为均是体仁之义。此则本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5H 页
 义不然。盖此朱子说。本是雍也仁而不佞章集注。而其下蔡氏说。主天理而言。以体用动静双举对说也。陈氏说主人工而言。以知行本末一条直说也。蔡说以为心之德爱之理六字。与全体不息四字。合为十字。而千古圣贤论仁。不出乎此。胡云峰剖判以为陈氏以体仁言。蔡氏以仁体言。朱子以为全体而不息者。而字者字。当属体仁。先正从胡说。以陈说为主。蔡说继补矣。此义精微。不可略过矣。且横渠说言有教动有法。春坊则以为当属省察。与下句瞬有养息有存相对看。此亦不然矣。省察与教法。自有工夫功效之别。省察学者一念初动处。卞其善恶邪正者。下学之工夫也。教法则既入善关。充足于己。为法于人者。成德之功效也。省察教法。不可合而观之。盖春坊之意。误看言动之动字。而谓属省察。此动字本兼动静。注说以德行言之。德行则不可专属于动。中庸以为以德行言之中庸是也。而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子已有定论。况此言动。本非下学之言动。其成德以后言动。不可偏属于省察。且存养偏言之则与省察相对。专言之则存养本兼省察。如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是也。此段存养中。实包省察。中
义不然。盖此朱子说。本是雍也仁而不佞章集注。而其下蔡氏说。主天理而言。以体用动静双举对说也。陈氏说主人工而言。以知行本末一条直说也。蔡说以为心之德爱之理六字。与全体不息四字。合为十字。而千古圣贤论仁。不出乎此。胡云峰剖判以为陈氏以体仁言。蔡氏以仁体言。朱子以为全体而不息者。而字者字。当属体仁。先正从胡说。以陈说为主。蔡说继补矣。此义精微。不可略过矣。且横渠说言有教动有法。春坊则以为当属省察。与下句瞬有养息有存相对看。此亦不然矣。省察与教法。自有工夫功效之别。省察学者一念初动处。卞其善恶邪正者。下学之工夫也。教法则既入善关。充足于己。为法于人者。成德之功效也。省察教法。不可合而观之。盖春坊之意。误看言动之动字。而谓属省察。此动字本兼动静。注说以德行言之。德行则不可专属于动。中庸以为以德行言之中庸是也。而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子已有定论。况此言动。本非下学之言动。其成德以后言动。不可偏属于省察。且存养偏言之则与省察相对。专言之则存养本兼省察。如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是也。此段存养中。实包省察。中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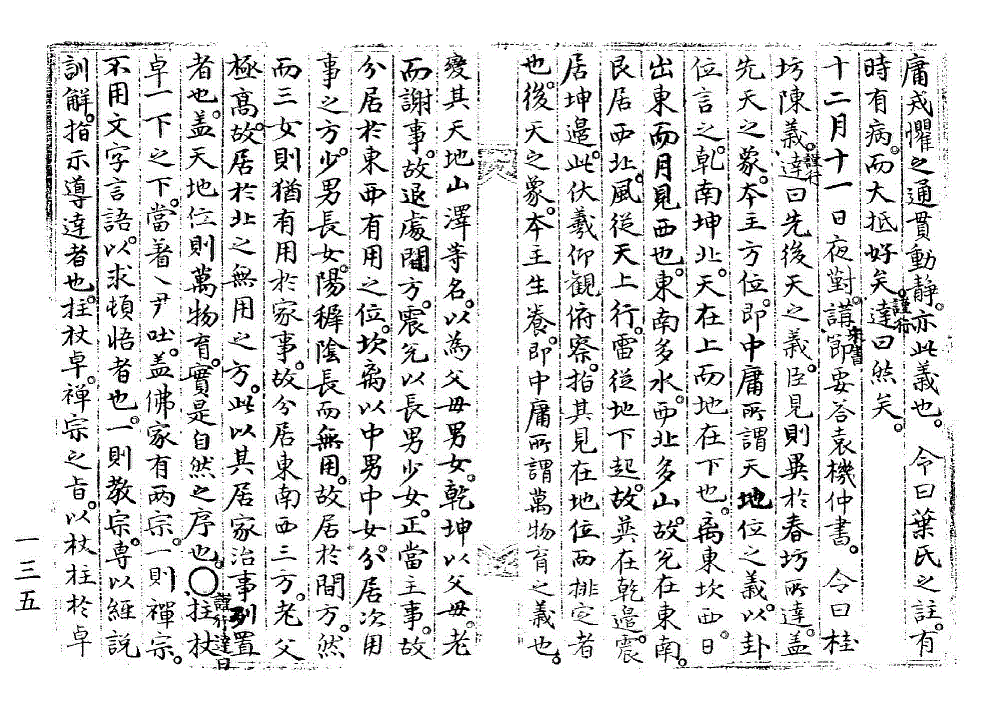 庸戒惧之通贯动静。亦此义也。 令曰叶氏之注。有时有病。而大抵好矣。谨行达曰然矣。
庸戒惧之通贯动静。亦此义也。 令曰叶氏之注。有时有病。而大抵好矣。谨行达曰然矣。十二月十一日夜对。讲朱书节要答袁机仲书。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先后天之义。臣见则异于春坊所达。盖先天之象。本主方位。即中庸所谓天地位之义。以卦位言之。乾南坤北。天在上而地在下也。离东坎西。日出东而月见西也。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故兑在东南。艮居西北。风从天上行。雷从地下起。故巽在乾边。震居坤边。此伏羲仰观俯察。指其见在地位而排定者也。后天之象。本主生养。即中庸所谓万物育之义也。变其天地山泽等名。以为父母男女。乾坤以父母。老而谢事。故退处间方。震兑以长男少女。正当主事。故分居于东西有用之位。坎离以中男中女。分居次用事之方。少男长女。阳稚阴长而无用。故居于间方。然而三女则犹有用于家事。故分居东南西三方。老父极高。故居于北之无用之方。此以其居家治事列置者也。盖天地位则万物育。实是自然之序也。○谨行达曰拄杖卓一下之下。当着吐。盖佛家有两宗。一则禅宗。不用文字言语。以求顿悟者也。一则教宗。专以经说训解。指示导达者也。拄杖卓。禅宗之旨。以杖拄于卓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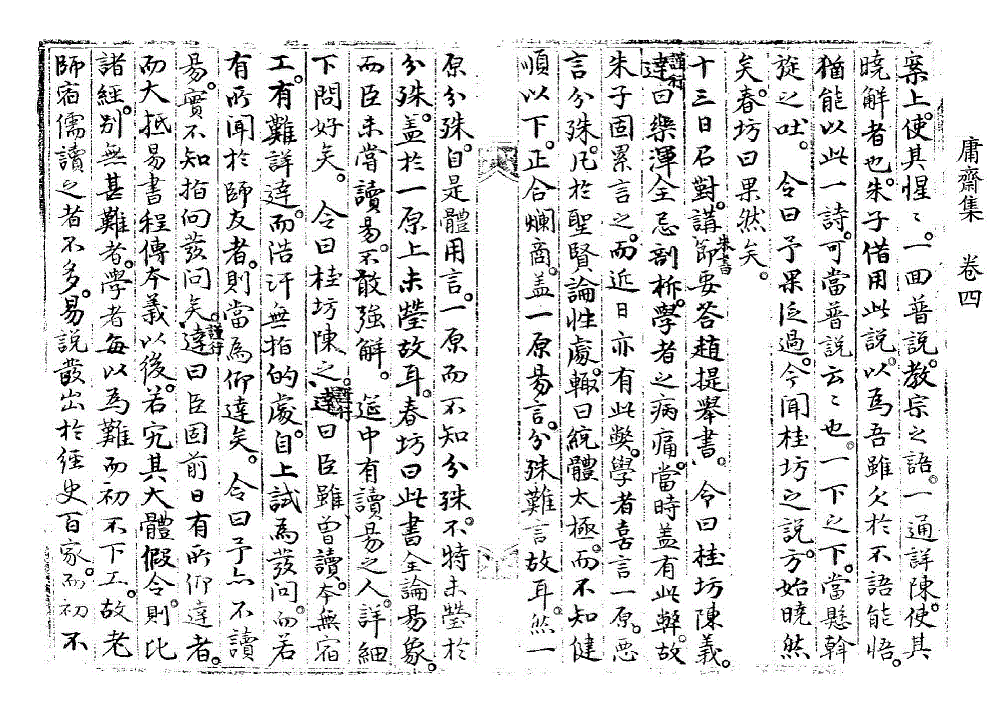 案上。使其惺惺。一回普说。教宗之语。一通详陈。使其晓解者也。朱子借用此说。以为吾虽欠于不语能悟。犹能以此一诗。可当普说云云也。一下之下。当悬斡旋之吐。 令曰予果泛过。今闻桂坊之说。方始晓然矣。春坊曰果然矣。
案上。使其惺惺。一回普说。教宗之语。一通详陈。使其晓解者也。朱子借用此说。以为吾虽欠于不语能悟。犹能以此一诗。可当普说云云也。一下之下。当悬斡旋之吐。 令曰予果泛过。今闻桂坊之说。方始晓然矣。春坊曰果然矣。十三日召对。讲朱书节要答赵提举书。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乐浑全忌剖析。学者之病痛。当时盖有此弊。故朱子固累言之。而近日亦有此弊。学者喜言一原。恶言分殊。凡于圣贤论性处。辄曰统体太极。而不知健顺以下。正合烂商。盖一原易言。分殊难言故耳。然一原分殊。自是体用言。一原而不知分殊。不特未莹于分殊。盖于一原上未莹故耳。春坊曰此书全论易象。而臣未尝读易。不敢强解。 筵中有读易之人。详细下问好矣。 令曰桂坊陈之。谨行达曰臣虽曾读。本无宿工。有难详达。而浩汗无指的处。自上试为发问。而若有所闻于师友者。则当为仰达矣。 令曰予亦不读易。实不知指向发问矣。谨行达曰臣固前日有所仰达者。而大抵易书程传本义以后。若宄(一作究)其大体假令。则比诸经。别无甚难者。学者每以为难而初不下工。故老师宿儒读之者不多。易说发出于经史百家。而初不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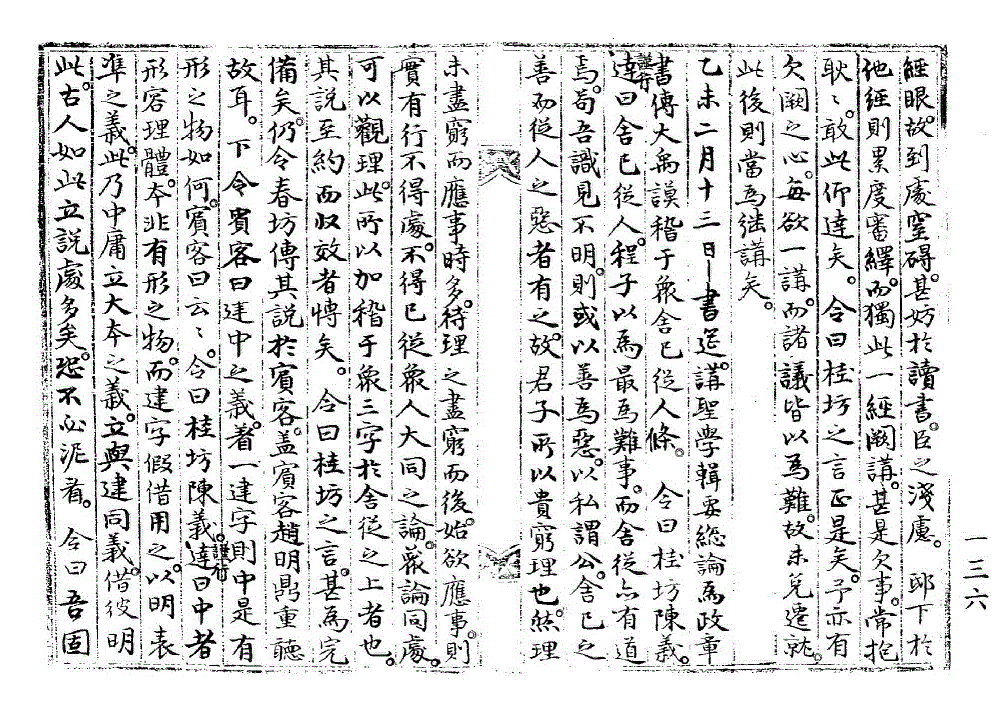 经眼。故到处窒碍。甚妨于读书。臣之浅虑。 邸下于他经则累度审绎。而独此一经阙讲。甚是欠事。常抱耿耿。敢此仰达矣。 令曰桂坊之言正是矣。予亦有欠阙之心。每欲一讲。而诸议皆以为难。故未免迁就。此后则当为继讲矣。
经眼。故到处窒碍。甚妨于读书。臣之浅虑。 邸下于他经则累度审绎。而独此一经阙讲。甚是欠事。常抱耿耿。敢此仰达矣。 令曰桂坊之言正是矣。予亦有欠阙之心。每欲一讲。而诸议皆以为难。故未免迁就。此后则当为继讲矣。乙未二月十三日书筵。讲圣学辑要总论为政章书传大禹谟稽于众舍己从人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舍己从人。程子以为最为难事。而舍从亦有道焉。苟吾识见不明。则或以善为恶。以私谓公。舍己之善而从人之恶者有之。故君子所以贵穷理也。然理未尽穷而应事时多。待理之尽穷而后。始欲应事。则实有行不得处。不得已从众人大同之论。众论同处。可以观理。此所以加稽于众三字于舍从之上者也。其说至约而收效者博矣。 令曰桂坊之言。甚为完备矣。仍令春坊传其说于宾客。盖宾客赵明鼎重听故耳。 下令宾客曰建中之义。着一建字则中是有形之物如何。宾客曰云云。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中者形容理体。本非有形之物。而建字假借用之。以明表准之义。此乃中庸立大本之义。立与建同义。借彼明此。古人如此立说处多矣。恐不必泥看。 令曰吾固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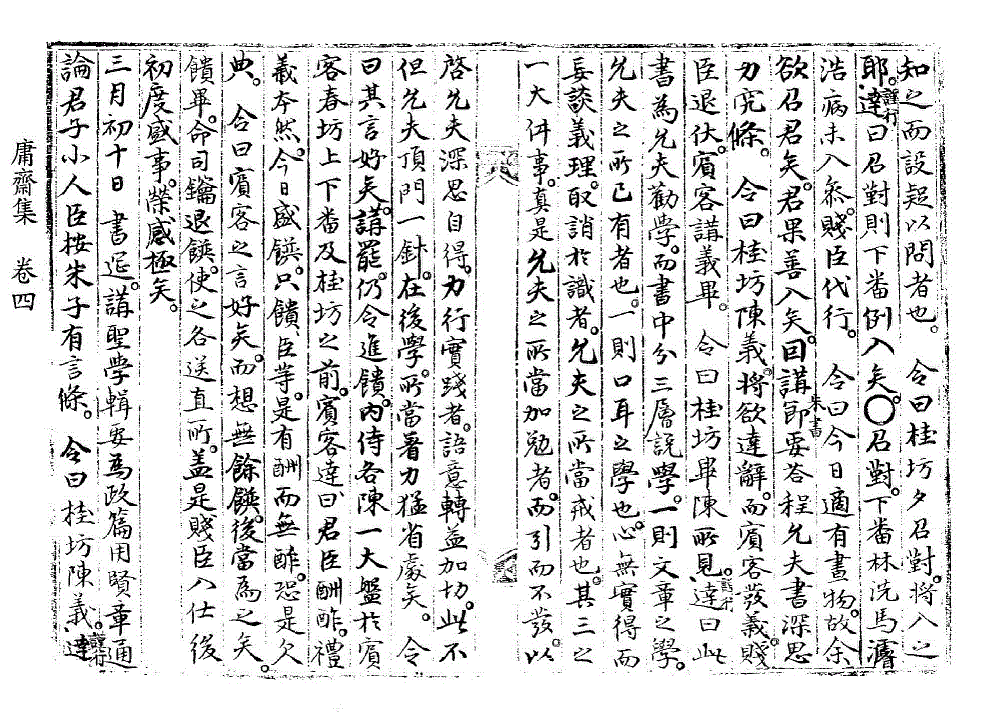 知之而设疑以问者也。 令曰桂坊夕召对。将入之耶。谨行达曰召对则下番例入矣。○召对。下番林洗马浚浩病未入参。贱臣代行。 令曰今日适有昼物。故余欲召君矣。君果善入矣。因讲朱书节要答程允夫书深思力究条。 令曰桂坊陈义。将欲达辞。而宾客发义。贱臣退伏。宾客讲义毕。 令曰桂坊毕陈所见。谨行达曰此书为允夫劝学。而书中分三层说学。一则文章之学。允夫之所已有者也。一则口耳之学也。心无实得而妄谈义理。取诮于识者。允夫之所当戒者也。其三之一大件事。真是允夫之所当加勉者。而引而不发。以启允夫深思自得。力行实践者。语意转益加切。此不但允夫顶门一针。在后学。所当着力猛省处矣。 令曰其言好矣。讲罢。仍令进馈。内侍各陈一大盘于宾客春坊上下番及桂坊之前。宾客达曰君臣酬酢。礼义本然。今日盛馔。只馈臣等。是有酬而无酢。恐是欠典。 令曰宾客之言好矣。而想无馀馔。后当为之矣。馈毕。命司钥退馔。使之各送直所。盖是贱臣入仕后初度盛事。荣感极矣。
知之而设疑以问者也。 令曰桂坊夕召对。将入之耶。谨行达曰召对则下番例入矣。○召对。下番林洗马浚浩病未入参。贱臣代行。 令曰今日适有昼物。故余欲召君矣。君果善入矣。因讲朱书节要答程允夫书深思力究条。 令曰桂坊陈义。将欲达辞。而宾客发义。贱臣退伏。宾客讲义毕。 令曰桂坊毕陈所见。谨行达曰此书为允夫劝学。而书中分三层说学。一则文章之学。允夫之所已有者也。一则口耳之学也。心无实得而妄谈义理。取诮于识者。允夫之所当戒者也。其三之一大件事。真是允夫之所当加勉者。而引而不发。以启允夫深思自得。力行实践者。语意转益加切。此不但允夫顶门一针。在后学。所当着力猛省处矣。 令曰其言好矣。讲罢。仍令进馈。内侍各陈一大盘于宾客春坊上下番及桂坊之前。宾客达曰君臣酬酢。礼义本然。今日盛馔。只馈臣等。是有酬而无酢。恐是欠典。 令曰宾客之言好矣。而想无馀馔。后当为之矣。馈毕。命司钥退馔。使之各送直所。盖是贱臣入仕后初度盛事。荣感极矣。三月初十日书筵。讲圣学辑要为政篇用贤章通论君子小人臣按朱子有言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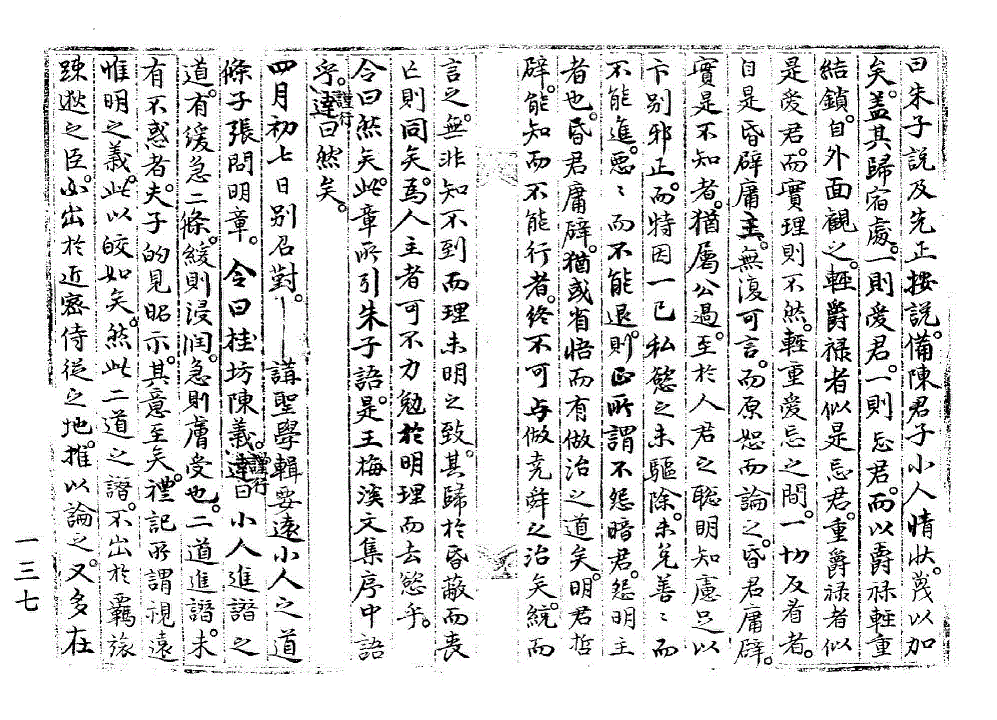 曰朱子说及先正按说。备陈君子小人情状。蔑以加矣。盖其归宿处。一则爱君。一则忘君。而以爵禄轻重结锁。自外面观之。轻爵禄者似是忘君。重爵禄者似是爱君。而实理则不然。轻重爱忘之间。一切反看者。自是昏辟庸主。无复可言。而原恕而论之。昏君庸辟。实是不知者。犹属公过。至于人君之聪明知虑足以卞别邪正。而特因一己私欲之未驱除。未免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退。则正所谓不怨暗君。怨明主者也。昏君庸辟。犹或省悟而有做治之道矣。明君哲辟。能知而不能行者。终不可与做尧舜之治矣。统而言之。无非知不到而理未明之致。其归于昏蔽而丧亡则同矣。为人主者可不力勉于明理而去欲乎。 令曰然矣。此章所引朱子语。是王梅溪文集序中语乎。谨行达曰然矣。
曰朱子说及先正按说。备陈君子小人情状。蔑以加矣。盖其归宿处。一则爱君。一则忘君。而以爵禄轻重结锁。自外面观之。轻爵禄者似是忘君。重爵禄者似是爱君。而实理则不然。轻重爱忘之间。一切反看者。自是昏辟庸主。无复可言。而原恕而论之。昏君庸辟。实是不知者。犹属公过。至于人君之聪明知虑足以卞别邪正。而特因一己私欲之未驱除。未免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退。则正所谓不怨暗君。怨明主者也。昏君庸辟。犹或省悟而有做治之道矣。明君哲辟。能知而不能行者。终不可与做尧舜之治矣。统而言之。无非知不到而理未明之致。其归于昏蔽而丧亡则同矣。为人主者可不力勉于明理而去欲乎。 令曰然矣。此章所引朱子语。是王梅溪文集序中语乎。谨行达曰然矣。四月初七日别召对。讲圣学辑要远小人之道条子张问明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小人进谮之道。有缓急二条。缓则浸润。急则肤受也。二道进谮。未有不惑者。夫子的见昭示。其意至矣。礼记所谓视远惟明之义。此以皎如矣。然此二道之谮。不出于羁旅疏逖之臣。必出于近密侍从之地。推以论之。又多在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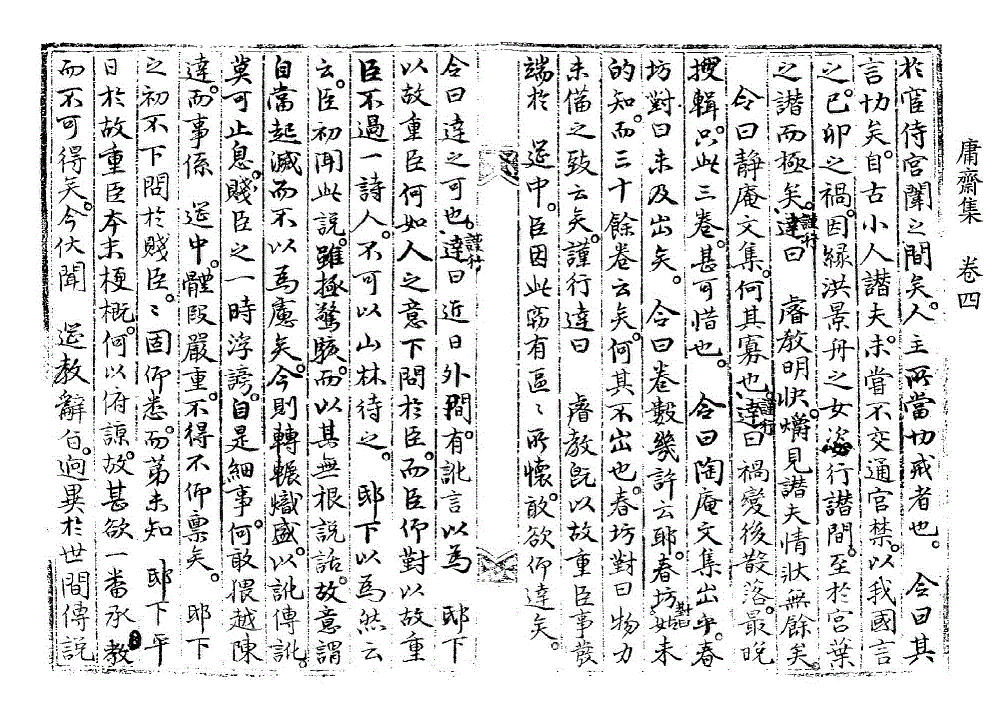 于宦侍宫闱之间矣。人主所当切戒者也。 令曰其言切矣。自古小人谮夫。未尝不交通宫禁。以我国言之。己卯之祸。因缘洪景舟之女恣行谮间。至于宫叶之谮而极矣。谨行达曰 睿教明快。爝见谮夫情状无馀矣。 令曰静庵文集。何其寡也。谨行达曰祸变后散落。最晚搜辑。只此三卷。甚可惜也。 令曰陶庵文集出乎。春坊对曰未及出矣。 令曰卷数几许云耶。春坊对曰姑未的知。而三十馀卷云矣。何其不出也。春坊对曰物力未备之致云矣。谨行达曰 睿教既以故重臣事发端于 筵中。臣因此窃有区区所怀。敢欲仰达矣。 令曰达之可也。谨行达曰近日外间。有讹言以为 邸下以故重臣何如人之意下问于臣。而臣仰对以故重臣不过一诗人。不可以山林待之。 邸下以为然云云。臣初闻此说。虽极惊骇。而以其无根说话。故意谓自当起灭而不以为虑矣。今则转辗炽盛。以讹传讹。莫可止息。贱臣之一时浮谤。自是细事。何敢猥越陈达。而事系 筵中。体段严重。不得不仰禀矣。 邸下之初不下问于贱臣。臣固仰悉。而第未知 邸下平日于故重臣本末梗概。何以俯谅。故甚欲一番承教而不可得矣。今伏闻 筵教辞旨。迥异于世间传说
于宦侍宫闱之间矣。人主所当切戒者也。 令曰其言切矣。自古小人谮夫。未尝不交通宫禁。以我国言之。己卯之祸。因缘洪景舟之女恣行谮间。至于宫叶之谮而极矣。谨行达曰 睿教明快。爝见谮夫情状无馀矣。 令曰静庵文集。何其寡也。谨行达曰祸变后散落。最晚搜辑。只此三卷。甚可惜也。 令曰陶庵文集出乎。春坊对曰未及出矣。 令曰卷数几许云耶。春坊对曰姑未的知。而三十馀卷云矣。何其不出也。春坊对曰物力未备之致云矣。谨行达曰 睿教既以故重臣事发端于 筵中。臣因此窃有区区所怀。敢欲仰达矣。 令曰达之可也。谨行达曰近日外间。有讹言以为 邸下以故重臣何如人之意下问于臣。而臣仰对以故重臣不过一诗人。不可以山林待之。 邸下以为然云云。臣初闻此说。虽极惊骇。而以其无根说话。故意谓自当起灭而不以为虑矣。今则转辗炽盛。以讹传讹。莫可止息。贱臣之一时浮谤。自是细事。何敢猥越陈达。而事系 筵中。体段严重。不得不仰禀矣。 邸下之初不下问于贱臣。臣固仰悉。而第未知 邸下平日于故重臣本末梗概。何以俯谅。故甚欲一番承教而不可得矣。今伏闻 筵教辞旨。迥异于世间传说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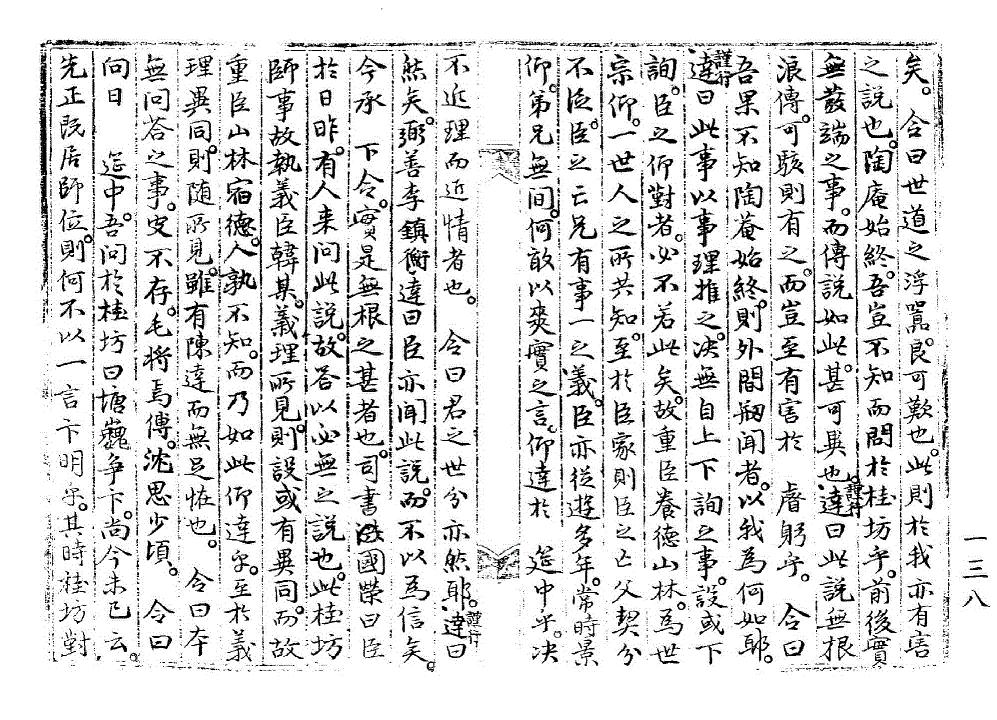 矣。 令曰世道之浮嚣。良可叹也。此则于我亦有害之说也。陶庵始终。吾岂不知而问于桂坊乎。前后实无发端之事。而传说如此。甚可异也。谨行达曰此说无根浪传。可骇则有之。而岂至有害于 睿躬乎。 令曰吾果不知陶庵始终。则外间刱闻者。以我为何如耶。谨行达曰此事以事理推之。决无自上下询之事。设或下询。臣之仰对者。必不若此矣。故重臣养德山林。为世宗仰。一世人之所共知。至于臣家则臣之亡父契分不泛。臣之亡兄有事一之义。臣亦从游多年。常时景仰。弟兄无间。何敢以爽实之言。仰达于 筵中乎。决不近理而近情者也。 令曰君之世分亦然耶。谨行达曰然矣。弼善李镇衡达曰臣亦闻此说。而不以为信矣。今承 下令。实是无根之甚者也。司书国荣曰臣于日昨。有人来问此说。故答以必无之说也。此桂坊师事故执义臣韩某。义理所见。则设或有异同。而故重臣山林宿德。人孰不知。而乃如此仰达乎。至于义理异同。则随所见。虽有陈达而无足怪也。 令曰本无问答之事。皮不存。毛将焉傅。沈思少顷。 令曰向日 筵中。吾问于桂坊曰塘巍争卞。尚今未已云。先正既居师位。则何不以一言卞明乎。其时桂坊对
矣。 令曰世道之浮嚣。良可叹也。此则于我亦有害之说也。陶庵始终。吾岂不知而问于桂坊乎。前后实无发端之事。而传说如此。甚可异也。谨行达曰此说无根浪传。可骇则有之。而岂至有害于 睿躬乎。 令曰吾果不知陶庵始终。则外间刱闻者。以我为何如耶。谨行达曰此事以事理推之。决无自上下询之事。设或下询。臣之仰对者。必不若此矣。故重臣养德山林。为世宗仰。一世人之所共知。至于臣家则臣之亡父契分不泛。臣之亡兄有事一之义。臣亦从游多年。常时景仰。弟兄无间。何敢以爽实之言。仰达于 筵中乎。决不近理而近情者也。 令曰君之世分亦然耶。谨行达曰然矣。弼善李镇衡达曰臣亦闻此说。而不以为信矣。今承 下令。实是无根之甚者也。司书国荣曰臣于日昨。有人来问此说。故答以必无之说也。此桂坊师事故执义臣韩某。义理所见。则设或有异同。而故重臣山林宿德。人孰不知。而乃如此仰达乎。至于义理异同。则随所见。虽有陈达而无足怪也。 令曰本无问答之事。皮不存。毛将焉傅。沈思少顷。 令曰向日 筵中。吾问于桂坊曰塘巍争卞。尚今未已云。先正既居师位。则何不以一言卞明乎。其时桂坊对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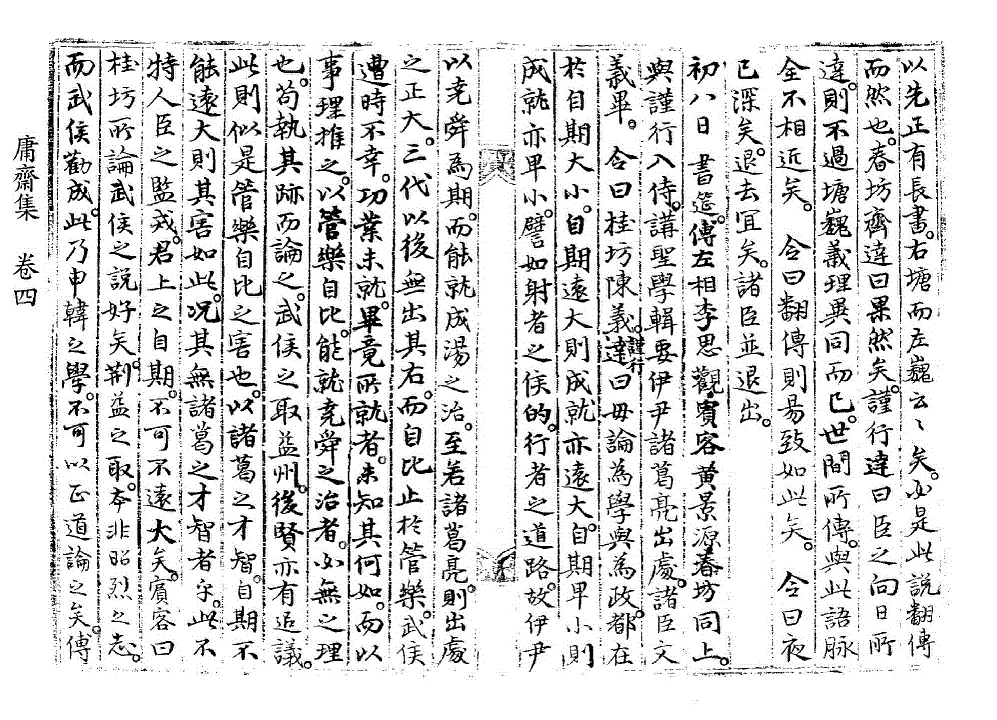 以先正有长书。右塘而左巍云云矣。必是此说翻传而然也。春坊齐达曰果然矣。谨行达曰臣之向日所达。则不过塘巍义理异同而已。世间所传。与此语脉全不相近矣。 令曰翻传则易致如此矣。 令曰夜已深矣。退去宜矣。诸臣并退出。
以先正有长书。右塘而左巍云云矣。必是此说翻传而然也。春坊齐达曰果然矣。谨行达曰臣之向日所达。则不过塘巍义理异同而已。世间所传。与此语脉全不相近矣。 令曰翻传则易致如此矣。 令曰夜已深矣。退去宜矣。诸臣并退出。初八日书筵。傅左相李思观,宾客黄景源,春坊同上。与谨行入侍。讲圣学辑要伊尹诸葛亮出处。诸臣文义毕。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毋论为学与为政。都在于自期大小。自期远大则成就亦远大。自期卑小则成就亦卑小。譬如射者之侯的。行者之道路。故伊尹以尧舜为期。而能就成汤之治。至若诸葛亮。则出处之正大。三代以后无出其右。而自比止于管乐。武侯遭时不幸。功业未就。毕竟所就者。未知其何如。而以事理推之。以管乐自比。能就尧舜之治者。必无之理也。苟执其迹而论之。武侯之取益州。后贤亦有追议。此则似是管乐自比之害也。以诸葛之才智。自期不能远大则其害如此。况其无诸葛之才智者乎。此不特人臣之监戒。君上之自期。不可不远大矣。宾客曰桂坊所论武侯之说好矣。荆益之取。本非昭烈之志。而武侯劝成。此乃申韩之学。不可以正道论之矣。傅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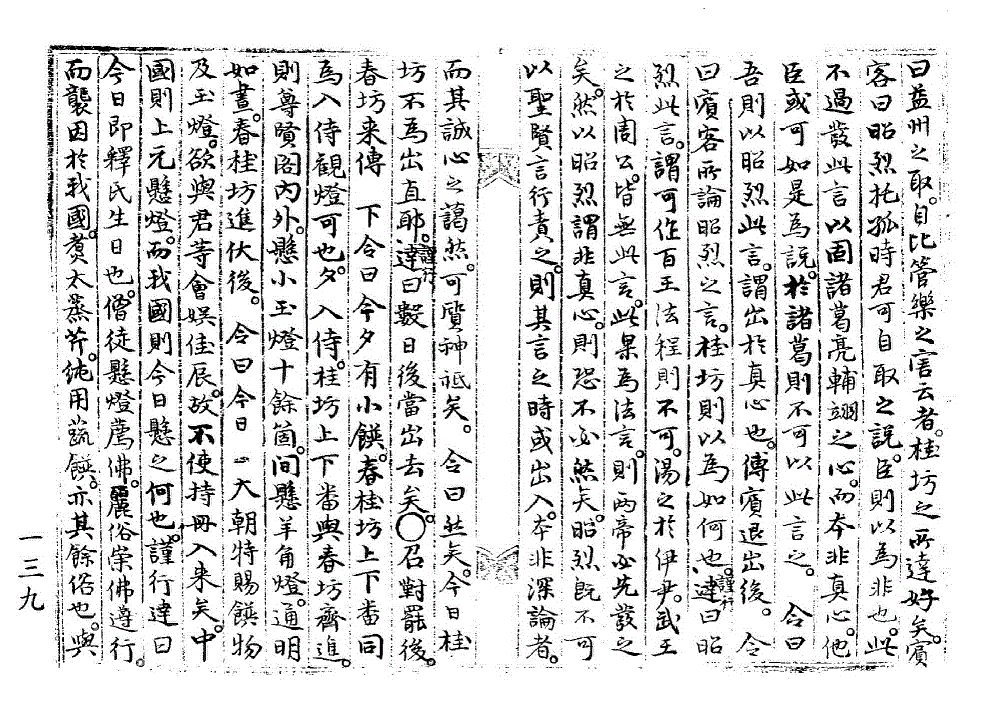 曰益州之取。自比管乐之害云者。桂坊之所达好矣。宾客曰昭烈托孤时君可自取之说。臣则以为非也。此不过发此言以固诸葛亮辅翊之心。而本非真心。他臣或可如是为说。于诸葛则不可以此言之。 令曰吾则以昭烈此言。谓出于真心也。傅宾退出后。 令曰宾客所论昭烈之言。桂坊则以为如何也。谨行达曰昭烈此言。谓可作百王法程则不可。汤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周公。皆无此言。此果为法言。则两帝必先发之矣。然以昭烈谓非真心。则恐不必然矣。昭烈既不可以圣贤言行责之。则其言之时或出入。本非深论者。而其诚心之蔼然。可质神祗矣。 令曰然矣。今日桂坊不为出直耶。谨行达曰数日后当出去矣。○召对罢后。春坊来传 下令曰今夕有小馔。春桂坊上下番同为入侍观灯可也。夕入侍。桂坊上下番与春坊齐进。则尊贤阁内外。悬小玉灯十馀个。间悬羊角灯。通明如昼。春桂坊进伏后。 令曰今日 大朝特赐馔物及玉灯。欲与君等会娱佳辰。故不使持册入来矣。中国则上元悬灯。而我国则今日悬之何也。谨行达曰今日即释氏生日也。僧徒悬灯荐佛。丽俗崇佛遵行。而袭因于我国。煮太蒸芹。纯用蔬馔。亦其馀俗也。与
曰益州之取。自比管乐之害云者。桂坊之所达好矣。宾客曰昭烈托孤时君可自取之说。臣则以为非也。此不过发此言以固诸葛亮辅翊之心。而本非真心。他臣或可如是为说。于诸葛则不可以此言之。 令曰吾则以昭烈此言。谓出于真心也。傅宾退出后。 令曰宾客所论昭烈之言。桂坊则以为如何也。谨行达曰昭烈此言。谓可作百王法程则不可。汤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周公。皆无此言。此果为法言。则两帝必先发之矣。然以昭烈谓非真心。则恐不必然矣。昭烈既不可以圣贤言行责之。则其言之时或出入。本非深论者。而其诚心之蔼然。可质神祗矣。 令曰然矣。今日桂坊不为出直耶。谨行达曰数日后当出去矣。○召对罢后。春坊来传 下令曰今夕有小馔。春桂坊上下番同为入侍观灯可也。夕入侍。桂坊上下番与春坊齐进。则尊贤阁内外。悬小玉灯十馀个。间悬羊角灯。通明如昼。春桂坊进伏后。 令曰今日 大朝特赐馔物及玉灯。欲与君等会娱佳辰。故不使持册入来矣。中国则上元悬灯。而我国则今日悬之何也。谨行达曰今日即释氏生日也。僧徒悬灯荐佛。丽俗崇佛遵行。而袭因于我国。煮太蒸芹。纯用蔬馔。亦其馀俗也。与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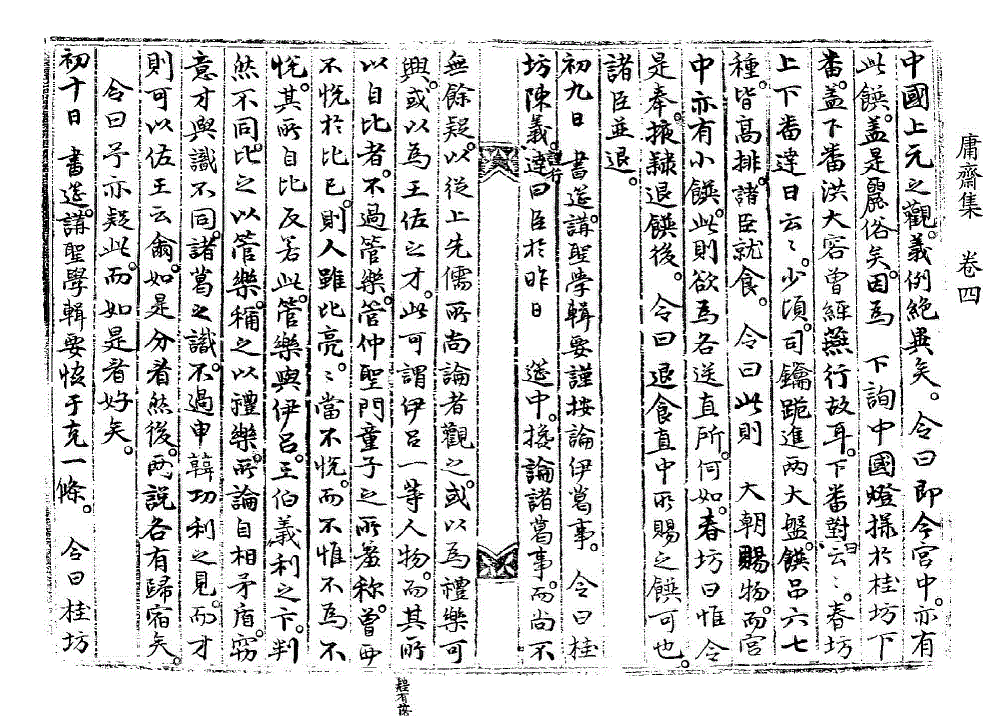 中国上元之观。义例绝异矣。 令曰即今宫中。亦有此馔。盖是丽俗矣。因为 下询中国灯㨾于桂坊下番。盖下番洪大容曾经燕行故耳。下番对曰云云。春坊上下番达曰云云。少顷。司钥跪进两大盘。馔品六七种。皆高排。诸臣就食。 令曰此则 大朝赐物。而宫中亦有小馔。此则欲为各送直所。何如。春坊曰惟令是奉。掖隶退馔后。 令曰退食直中所赐之馔可也。诸臣并退。
中国上元之观。义例绝异矣。 令曰即今宫中。亦有此馔。盖是丽俗矣。因为 下询中国灯㨾于桂坊下番。盖下番洪大容曾经燕行故耳。下番对曰云云。春坊上下番达曰云云。少顷。司钥跪进两大盘。馔品六七种。皆高排。诸臣就食。 令曰此则 大朝赐物。而宫中亦有小馔。此则欲为各送直所。何如。春坊曰惟令是奉。掖隶退馔后。 令曰退食直中所赐之馔可也。诸臣并退。初九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谨按论伊葛事。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臣于昨日 筵中。搀论诸葛事。而尚不无馀疑。以从上先儒所尚论者观之。或以为礼乐可兴。或以为王佐之才。此可谓伊吕一等人物。而其所以自比者。不过管乐。管仲圣门童子之所羞称。曾西不悦于比己。则人虽比亮。亮当不悦。而不惟不为不悦。其所自比反若此。管乐与伊吕。王伯义利之卞。判然不同。比之以管乐。称之以礼乐。所论自相矛盾。窃意才与识不同。诸葛之识。不过申韩功利之见。而才则可以佐王云尔。如是分看然后。两说各有归宿矣。 令曰予亦疑此。而如是看好矣。
初十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协于克一条。 令曰桂坊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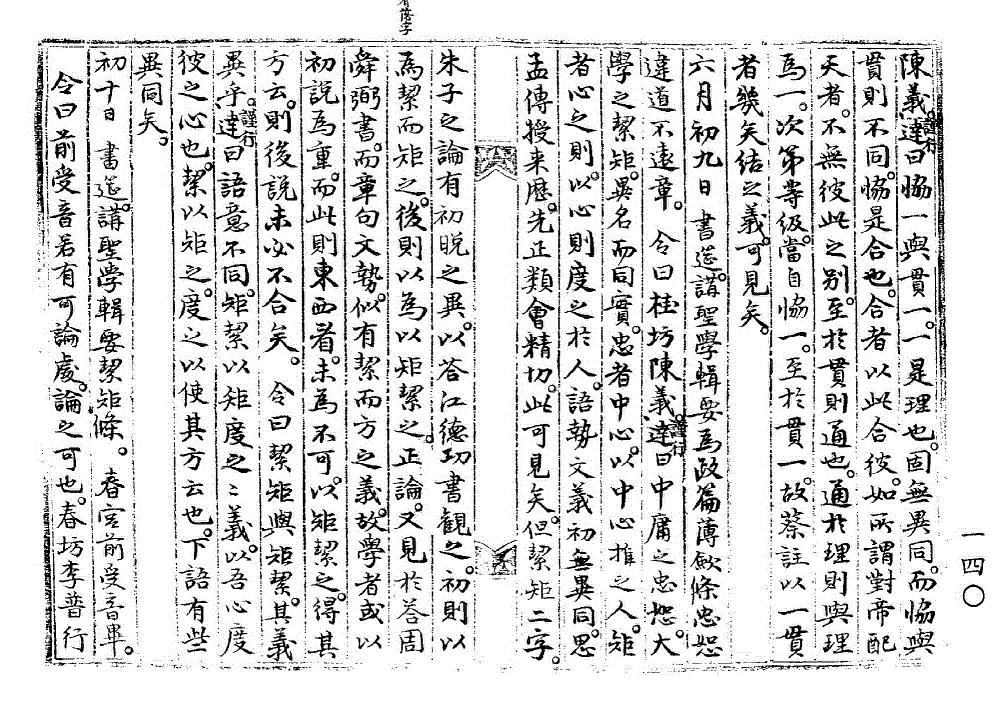 陈义。谨行达曰协一与贯一。一是理也。固无异同。而协与贯则不同。协是合也。合者以此合彼。如所谓对帝配天者。不无彼此之别。至于贯则通也。通于理则与理为一。次第等级。当自协一。至于贯一。故蔡注以一贯者几矣结之义。可见矣。
陈义。谨行达曰协一与贯一。一是理也。固无异同。而协与贯则不同。协是合也。合者以此合彼。如所谓对帝配天者。不无彼此之别。至于贯则通也。通于理则与理为一。次第等级。当自协一。至于贯一。故蔡注以一贯者几矣结之义。可见矣。六月初九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为政篇薄敛条忠恕违道不远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中庸之忠恕。大学之絜矩。异名而同实。忠者中心。以中心推之人。矩者心之则。以心则度之于人。语势文义初无异同。思孟传授来历。先正类会精切。此可见矣。但絜矩二字。朱子之论有初晚之异。以答江德功书观之。初则以为絜而矩之。后则以为以矩絜之주-D002。正论。又见于答周舜弼书。而章句文势。似有絜而方之义。故学者或以初说为重。而此则东西看。未为不可。以矩絜之。得其方云。则后说未必不合矣。 令曰絜矩与矩絜。其义异乎。谨行达曰语意不同。矩絜以矩度之之义。以吾心度彼之心也。絜以矩之。度之以使其方云也。下语有些异同矣。
初十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絜矩条。春宫前受音毕。 令曰前受音若有可论处。论之可也。春坊李普行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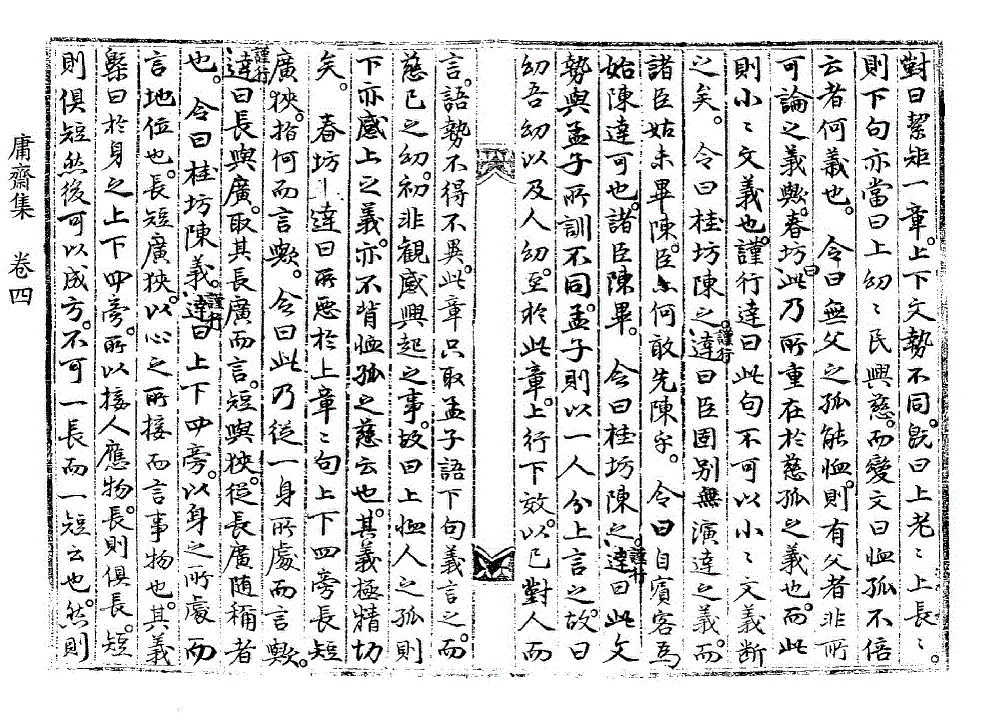 对曰絜矩一章。上下文势不同。既曰上老老上长长。则下句亦当曰上幼幼民兴慈。而变文曰恤孤不倍云者何义也。 令曰无父之孤能恤。则有父者非所可论之义欤。春坊曰此乃所重在于慈孤之义也。而此则小小文义也。谨行达曰此句不可以小小文义断之矣。 令曰桂坊陈之。谨行达曰臣固别无演达之义。而诸臣姑未毕陈。臣何敢先陈乎。 令曰自宾客为始陈达可也。诸臣陈毕。 令曰桂坊陈之。谨行达曰此文势与孟子所训不同。孟子则以一人分上言之。故曰幼吾幼以及人幼。至于此章。上行下效。以己对人而言。语势不得不异。此章只取孟子语下句义言之。而慈己之幼。初非观感兴起之事。故曰上恤人之孤则下亦感上之义。亦不背恤孤之慈云也。其义极精切矣。 春坊达曰所恶于上章章句上下四旁长短广狭。指何而言欤。 令曰此乃从一身所处而言欤。谨行达曰长与广。取其长广而言。短与狭。从长广随称者也。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上下四旁。以身之所处而言地位也。长短广狭。以心之所接而言事物也。其义槩曰于身之上下四旁。所以接人应物。长则俱长。短则俱短然后可以成方。不可一长而一短云也。然则
对曰絜矩一章。上下文势不同。既曰上老老上长长。则下句亦当曰上幼幼民兴慈。而变文曰恤孤不倍云者何义也。 令曰无父之孤能恤。则有父者非所可论之义欤。春坊曰此乃所重在于慈孤之义也。而此则小小文义也。谨行达曰此句不可以小小文义断之矣。 令曰桂坊陈之。谨行达曰臣固别无演达之义。而诸臣姑未毕陈。臣何敢先陈乎。 令曰自宾客为始陈达可也。诸臣陈毕。 令曰桂坊陈之。谨行达曰此文势与孟子所训不同。孟子则以一人分上言之。故曰幼吾幼以及人幼。至于此章。上行下效。以己对人而言。语势不得不异。此章只取孟子语下句义言之。而慈己之幼。初非观感兴起之事。故曰上恤人之孤则下亦感上之义。亦不背恤孤之慈云也。其义极精切矣。 春坊达曰所恶于上章章句上下四旁长短广狭。指何而言欤。 令曰此乃从一身所处而言欤。谨行达曰长与广。取其长广而言。短与狭。从长广随称者也。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上下四旁。以身之所处而言地位也。长短广狭。以心之所接而言事物也。其义槩曰于身之上下四旁。所以接人应物。长则俱长。短则俱短然后可以成方。不可一长而一短云也。然则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1L 页
 所谓长短广狭者。本就事物上平说。非如是非邪正之云也。春坊达曰桂坊所陈是矣。臣之所达则误矣。听言之道。只在于言之得失。不必以春坊所达为尽是。桂坊使之尽言而详纳之。是臣所望于邸下者也。宾客黄景源达曰此桂坊有渊源。有笃实工夫。今者所达。犹未尽分。 邸下详问而使之尽言。 令曰此桂坊出入 筵中久矣。予所详知者。实是最难之士也。○讲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大学絜矩一章。三言得失。语益加切。自公好恶三字。实为絜矩本领。而此章详言得失之本。结之以所欲与所恶。公好恶之意也。其传授之义可知。其前后一揆矣。但下章以生道杀民。分属于好恶。则或以为当属所欲。或以为当属所恶。有甲乙之不同矣。 令曰似当属于所恶矣。桂坊则以为如何。谨行达曰臣则以为甲说似长矣。盖杀民二字。似属于所恶。而杀人而恶死。过恶之甚者。此不可以好恶论得。且上章文义所欲与之。所恶勿施。生道杀民。本非勿施之事。故此句当属所欲矣。 令曰宾客之意何如。宾客对曰圣人之杀民。盖出于不获已。必欲傅之生议。而终无奈可生之道故杀之。此岂非所欲之类乎。 令曰残暴众
所谓长短广狭者。本就事物上平说。非如是非邪正之云也。春坊达曰桂坊所陈是矣。臣之所达则误矣。听言之道。只在于言之得失。不必以春坊所达为尽是。桂坊使之尽言而详纳之。是臣所望于邸下者也。宾客黄景源达曰此桂坊有渊源。有笃实工夫。今者所达。犹未尽分。 邸下详问而使之尽言。 令曰此桂坊出入 筵中久矣。予所详知者。实是最难之士也。○讲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章。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大学絜矩一章。三言得失。语益加切。自公好恶三字。实为絜矩本领。而此章详言得失之本。结之以所欲与所恶。公好恶之意也。其传授之义可知。其前后一揆矣。但下章以生道杀民。分属于好恶。则或以为当属所欲。或以为当属所恶。有甲乙之不同矣。 令曰似当属于所恶矣。桂坊则以为如何。谨行达曰臣则以为甲说似长矣。盖杀民二字。似属于所恶。而杀人而恶死。过恶之甚者。此不可以好恶论得。且上章文义所欲与之。所恶勿施。生道杀民。本非勿施之事。故此句当属所欲矣。 令曰宾客之意何如。宾客对曰圣人之杀民。盖出于不获已。必欲傅之生议。而终无奈可生之道故杀之。此岂非所欲之类乎。 令曰残暴众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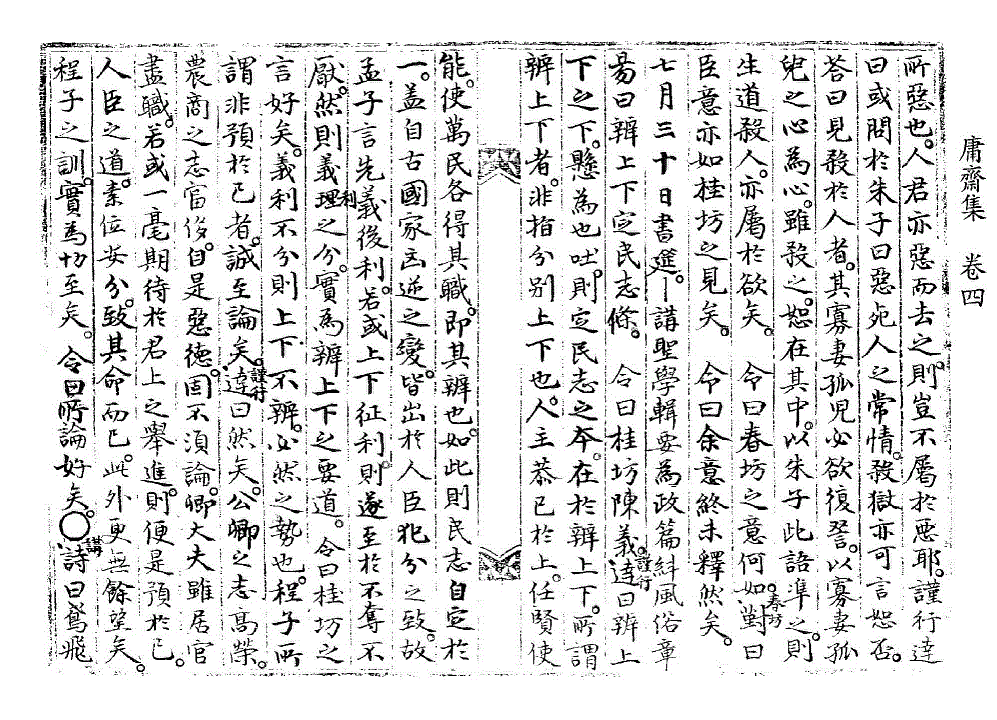 所恶也。人君亦恶而去之。则岂不属于恶耶。谨行达曰或问于朱子曰恶死人之常情。杀狱亦可言恕否。答曰见杀于人者。其寡妻孤儿必欲复雠。以寡妻孤儿之心为心。虽杀之。恕在其中。以朱子此语准之。则生道杀人。亦属于欲矣。 令曰春坊之意何如。春坊对曰臣意亦如桂坊之见矣。 令曰余意终未释然矣。
所恶也。人君亦恶而去之。则岂不属于恶耶。谨行达曰或问于朱子曰恶死人之常情。杀狱亦可言恕否。答曰见杀于人者。其寡妻孤儿必欲复雠。以寡妻孤儿之心为心。虽杀之。恕在其中。以朱子此语准之。则生道杀人。亦属于欲矣。 令曰春坊之意何如。春坊对曰臣意亦如桂坊之见矣。 令曰余意终未释然矣。七月三十日书筵。讲圣学辑要为政篇纠风俗章易曰辨上下定民志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辨上下之下。悬为也吐。则定民志之本。在于辨上下。所谓辨上下者。非指分别上下也。人主恭己于上。任贤使能。使万民各得其职。即其辨也。如此则民志自定于一。盖自古国家凶逆之变。皆出于人臣犯分之致。故孟子言先义后利。若或上下征利。则遂至于不夺不厌。然则义利之分。实为辨上下之要道。 令曰桂坊之言好矣。义利不分则上下不辨。必然之势也。程子所谓非预于己者。诚至论矣。谨行达曰然矣。公卿之志高荣。农商之志富侈。自是恶德。固不须论。卿大夫虽居官尽职。若或一毫期待于君上之举进。则便是预于己。人臣之道。素位安分。致其命而已。此外更无馀望矣。程子之训。实为切至矣。 令曰所论好矣。○讲诗曰鸢飞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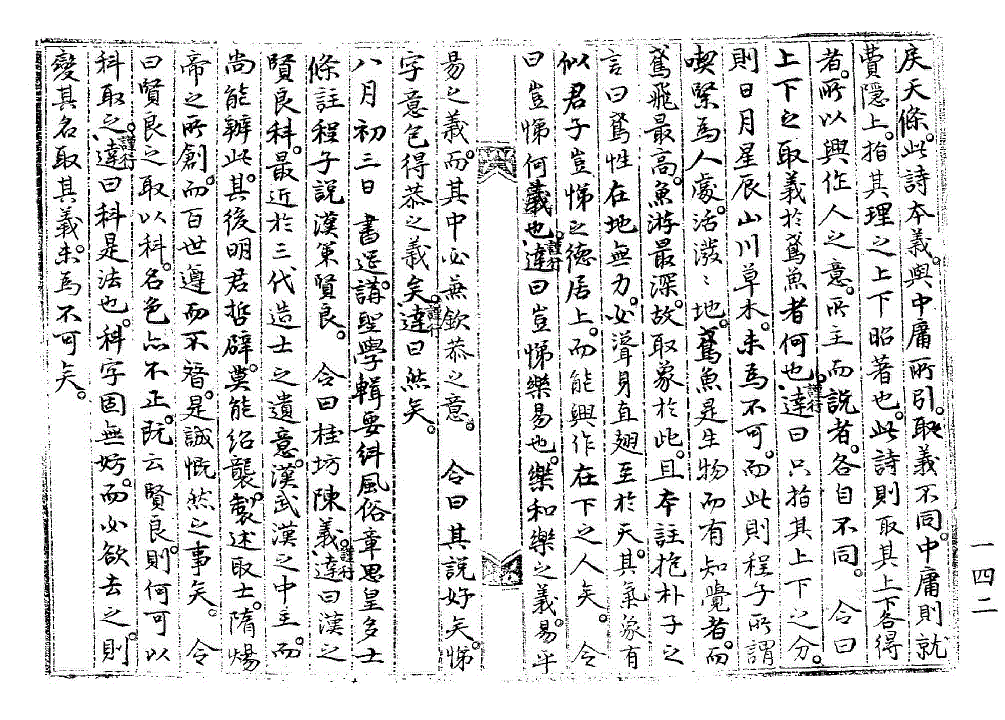 戾天条。此诗本义。与中庸所引。取义不同。中庸则就费隐上。指其理之上下昭著也。此诗则取其上下各得者。所以兴作人之意。所主而说者。各自不同。 令曰上下之取义于鸢鱼者何也。谨行达曰只指其上下之分。则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未为不可。而此则程子所谓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鸢鱼是生物而有知觉者。而鸢飞最高。鱼游最深。故取象于此。且本注抱朴子之言曰鸢性在地无力。必耸身直翅至于天。其气象有似君子岂悌之德居上。而能兴作在下之人矣。 令曰岂悌何义也。谨行达曰岂悌乐易也。乐和乐之义。易平易之义。而其中必兼钦恭之意。 令曰其说好矣。悌字意包得恭之义矣。谨行达曰然矣。
戾天条。此诗本义。与中庸所引。取义不同。中庸则就费隐上。指其理之上下昭著也。此诗则取其上下各得者。所以兴作人之意。所主而说者。各自不同。 令曰上下之取义于鸢鱼者何也。谨行达曰只指其上下之分。则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未为不可。而此则程子所谓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鸢鱼是生物而有知觉者。而鸢飞最高。鱼游最深。故取象于此。且本注抱朴子之言曰鸢性在地无力。必耸身直翅至于天。其气象有似君子岂悌之德居上。而能兴作在下之人矣。 令曰岂悌何义也。谨行达曰岂悌乐易也。乐和乐之义。易平易之义。而其中必兼钦恭之意。 令曰其说好矣。悌字意包得恭之义矣。谨行达曰然矣。八月初三日 书筵。讲圣学辑要纠风俗章思皇多士条注程子说汉策贤良。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汉之贤良科。最近于三代造士之遗意。汉武汉之中主。而尚能办此。其后明君哲辟。莫能绍袭。制述取士。隋炀帝之所创。而百世遵而不替。是诚慨然之事矣。 令曰贤良之取以科。名色亦不正。既云贤良。则何可以科取之。谨行达曰科是法也。科字固无妨。而必欲去之。则变其名取其义。未为不可矣。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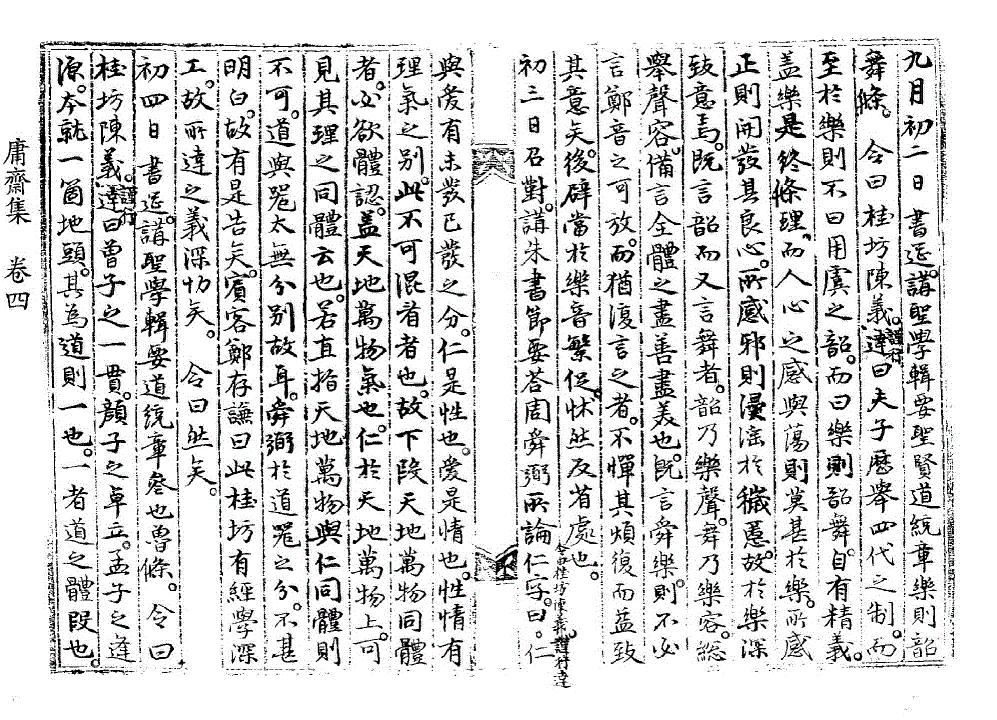 九月初二日书筵。讲圣学辑要圣贤道统章乐则韶舞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夫子历举四代之制。而至于乐则不曰用虞之韶。而曰乐则韶舞。自有精义。盖乐是终条理。而人心之感与荡则莫甚于乐。所感正则开发其良心。所感邪则漫淫于秽慝。故于乐深致意焉。既言韶而又言舞者。韶乃乐声。舞乃乐容。总举声容。备言全体之尽善尽美也。既言舜乐。则不必言郑音之可放。而犹复言之者。不惮其烦复而益致其意矣。后辟当于乐音繁促。怵然反省处也。
九月初二日书筵。讲圣学辑要圣贤道统章乐则韶舞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夫子历举四代之制。而至于乐则不曰用虞之韶。而曰乐则韶舞。自有精义。盖乐是终条理。而人心之感与荡则莫甚于乐。所感正则开发其良心。所感邪则漫淫于秽慝。故于乐深致意焉。既言韶而又言舞者。韶乃乐声。舞乃乐容。总举声容。备言全体之尽善尽美也。既言舜乐。则不必言郑音之可放。而犹复言之者。不惮其烦复而益致其意矣。后辟当于乐音繁促。怵然反省处也。初三日召对。讲朱书节要答周舜弼所论仁字。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仁与爱有未发已发之分。仁是性也。爱是情也。性情有理气之别。此不可混看者也。故下段天地万物同体者。必欲体认。盖天地万物气也。仁于天地万物上。可见其理之同体云也。若直指天地万物与仁同体则不可。道与器太无分别故耳。舜弼于道器之分。不甚明白。故有是告矣。宾客郑存谦曰此桂坊有经学深工。故所达之义深切矣。 令曰然矣。
初四日书筵。讲圣学辑要道统章参也鲁条。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曾子之一贯。颜子之卓立。孟子之逢源。本就一个地头。其为道则一也。一者道之体段也。
庸斋先生文集卷之四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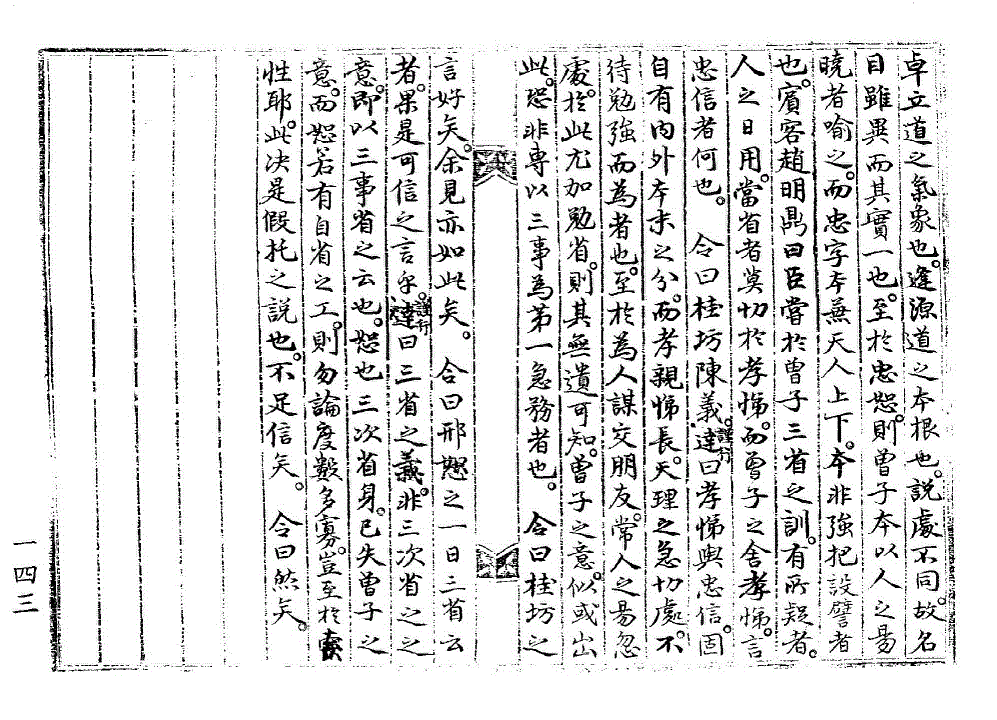 卓立道之气象也。逢源道之本根也。说处不同。故名目虽异而其实一也。至于忠恕。则曾子本以人之易晓者喻之。而忠字本兼天人上下。本非强把设譬者也。宾客赵明鼎曰臣尝于曾子三省之训。有所疑者。人之日用。当省者莫切于孝悌。而曾子之舍孝悌。言忠信者何也。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孝悌与忠信。固自有内外本末之分。而孝亲悌长。天理之急切处。不待勉强而为者也。至于为人谋交朋友。常人之易忽处。于此尤加勉省。则其无遗可知。曾子之意。似或出此。恐非专以三事为第一急务者也。 令曰桂坊之言好矣。余见亦如此矣。 令曰邢恕之一日三省云者。果是可信之言乎。谨行达曰三省之义。非三次省之之意。即以三事省之云也。恕也三次省身。已失曾子之意。而恕若有自省之工。则勿论度数多寡。岂至于索性耶。此决是假托之说也。不足信矣。 令曰然矣。
卓立道之气象也。逢源道之本根也。说处不同。故名目虽异而其实一也。至于忠恕。则曾子本以人之易晓者喻之。而忠字本兼天人上下。本非强把设譬者也。宾客赵明鼎曰臣尝于曾子三省之训。有所疑者。人之日用。当省者莫切于孝悌。而曾子之舍孝悌。言忠信者何也。 令曰桂坊陈义。谨行达曰孝悌与忠信。固自有内外本末之分。而孝亲悌长。天理之急切处。不待勉强而为者也。至于为人谋交朋友。常人之易忽处。于此尤加勉省。则其无遗可知。曾子之意。似或出此。恐非专以三事为第一急务者也。 令曰桂坊之言好矣。余见亦如此矣。 令曰邢恕之一日三省云者。果是可信之言乎。谨行达曰三省之义。非三次省之之意。即以三事省之云也。恕也三次省身。已失曾子之意。而恕若有自省之工。则勿论度数多寡。岂至于索性耶。此决是假托之说也。不足信矣。 令曰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