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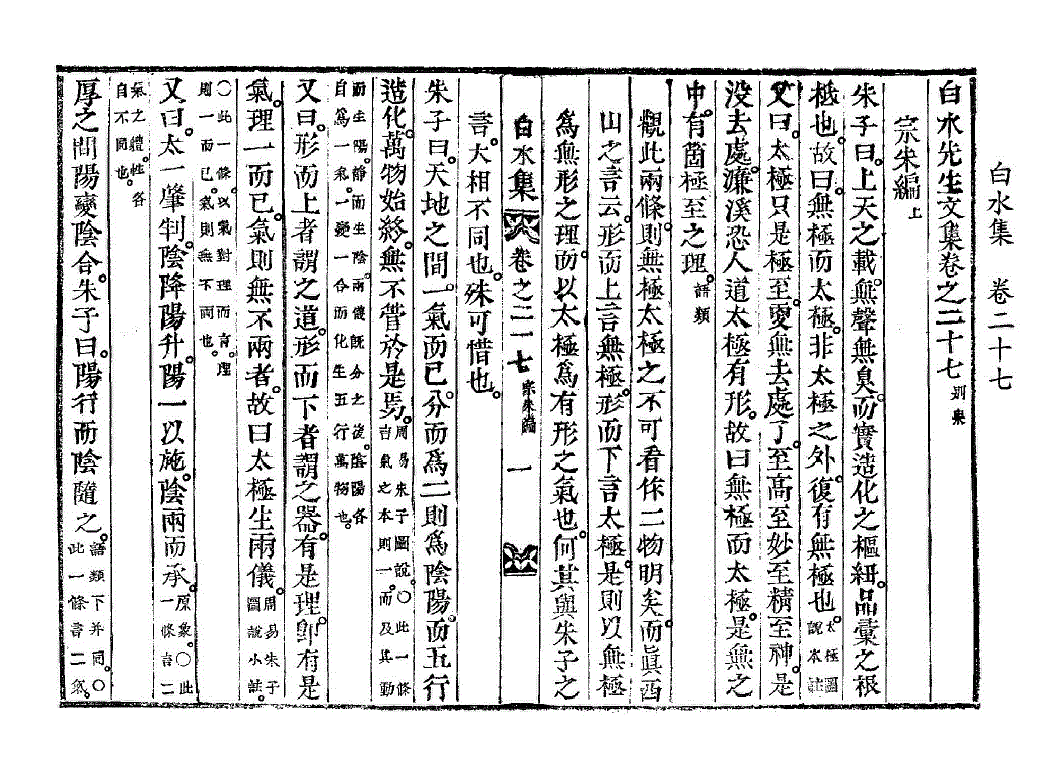 宗朱编[上]
宗朱编[上]朱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图说本注)又曰。太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极至之理。(语类)
观此两条。则无极太极之不可看作二物明矣。而真西山之言云。形而上言无极。形而下言太极。是则以无极为无形之理。而以太极为有形之气也。何其与朱子之言。大相不同也。殊可惜也。
朱子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周易朱子图说。○此一条言气之本则一。而及其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两仪既分之后。阴阳各自为一气。一变一合而化生五行万物也。)
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是理。即有是气。理一而已。气则无不两者。故曰太极生两仪。(周易朱子图说小注。○此一条。以气对理而言。理则一而已。气则无不两也。)
又曰。太一肇判。阴降阳升。阳一以施。阴两而承。(原象。○此一条言二气之体。性各自不同也。)
厚之问阳变阴合。朱子曰。阳行而阴随之。(语类下并同。○此一条言二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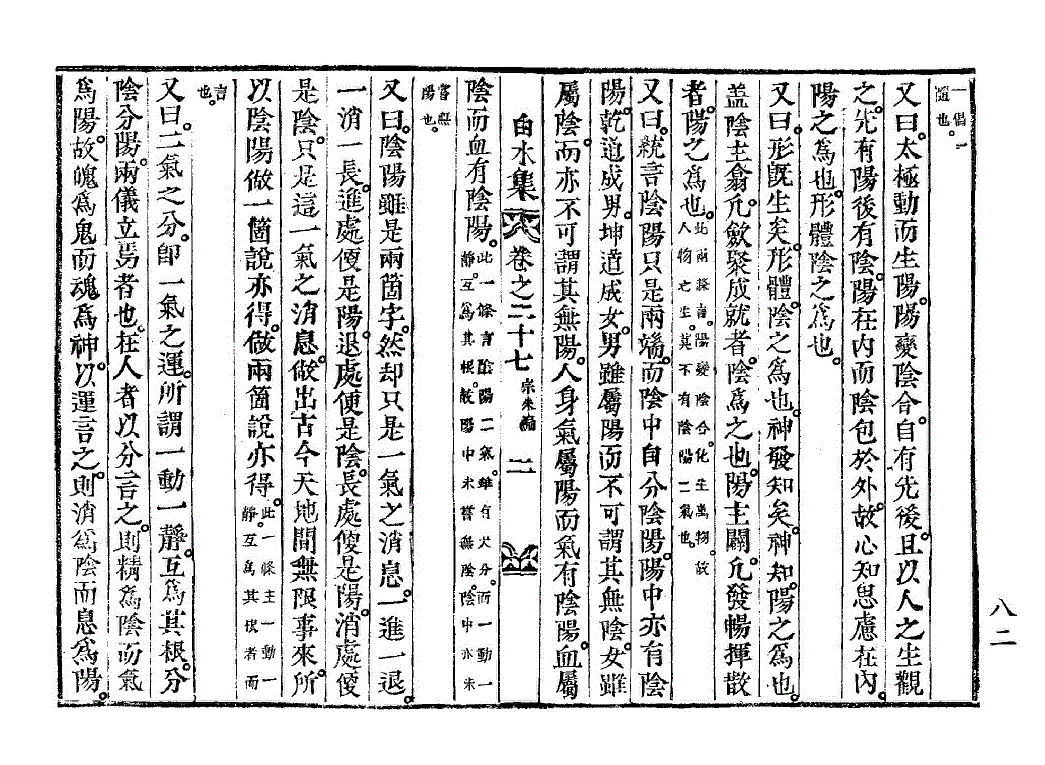 一倡一随也。)
一倡一随也。)又曰。太极动而生阳。阳变阴合。自有先后。且以人之生观之。先有阳后有阴。阳在内而阴包于外。故心知思虑在内。阳之为也。形体阴之为也。
又曰。形既生矣。形体。阴之为也。神发知矣。神知。阳之为也。盖阴主翕。凡敛聚成就者。阴为之也。阳主辟。凡发畅挥散者。阳之为也。(此两条言。阳变阴合。化生万物。故人物之生。莫不有阴阳二气也。)
又曰。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而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此一条言阴阳二气。虽有大分。而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故阳中未尝无阴。阴中亦未尝无阳也。)
又曰。阴阳虽是两个字。然却只是一气之消息。一进一退。一消一长。进处便是阳。退处便是阴。长处便是阳。消处便是阴。只是这一气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间无限事来。所以阴阳做一个说亦得。做两个说亦得。(此一条主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而言也。)
又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则精为阴而气为阳。故魄为鬼而魂为神。以运言之。则消为阴而息为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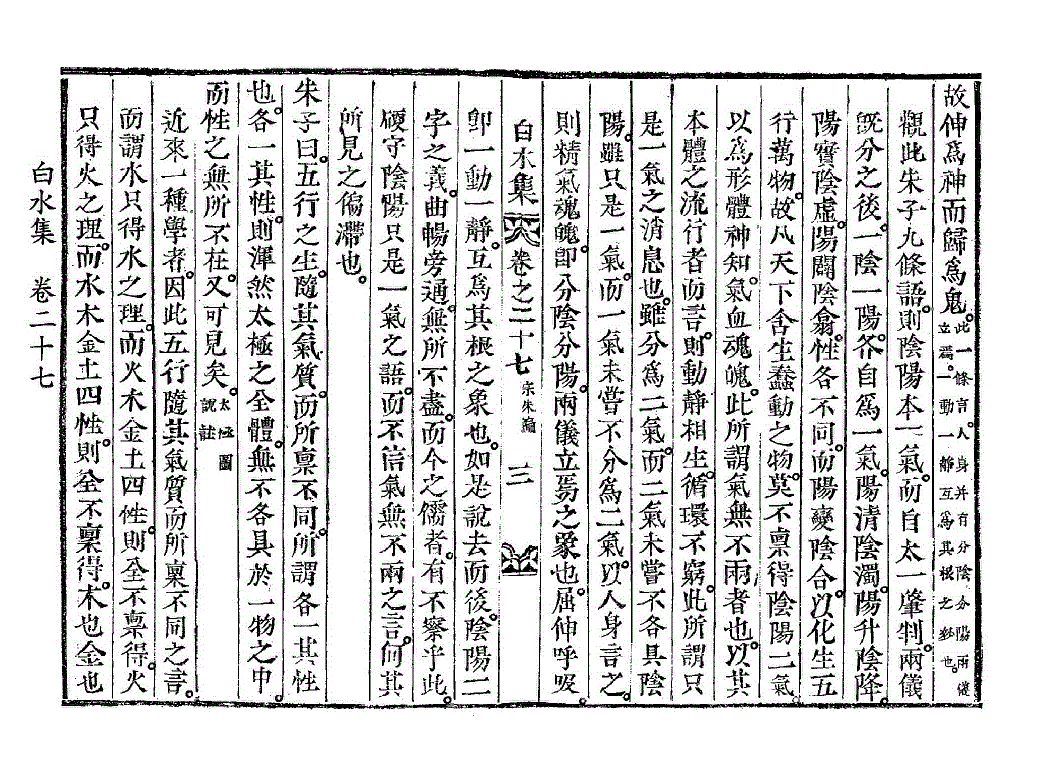 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一条言。人身并有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妙也。)
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一条言。人身并有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妙也。)观此朱子九条语。则阴阳本一气。而自太一肇判。两仪既分之后。一阴一阳。各自为一气。阳清阴浊。阳升阴降。阳实阴虚。阳辟阴翕。性各不同。而阳变阴合。以化生五行万物。故凡天下含生蠢动之物。莫不禀得阴阳二气。以为形体神知。气血魂魄。此所谓气无不两者也。以其本体之流行者而言。则动静相生。循环不穷。此所谓只是一气之消息也。虽分为二气。而二气未尝不各具阴阳。虽只是一气。而一气未尝不分为二气。以人身言之。则精气魂魄。即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象也。屈伸呼吸。即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象也。如是说去而后。阴阳二字之义。曲畅旁通。无所不尽。而今之儒者。有不察乎此。硬守阴阳只是一气之语。而不信气无不两之言。何其所见之偏滞也。
朱子曰。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太极图说注)
近来一种学者。因此五行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之言。而谓水只得水之理。而火木金土四性。则全不禀得。火只得火之理。而水木金土四性。则全不禀得。木也金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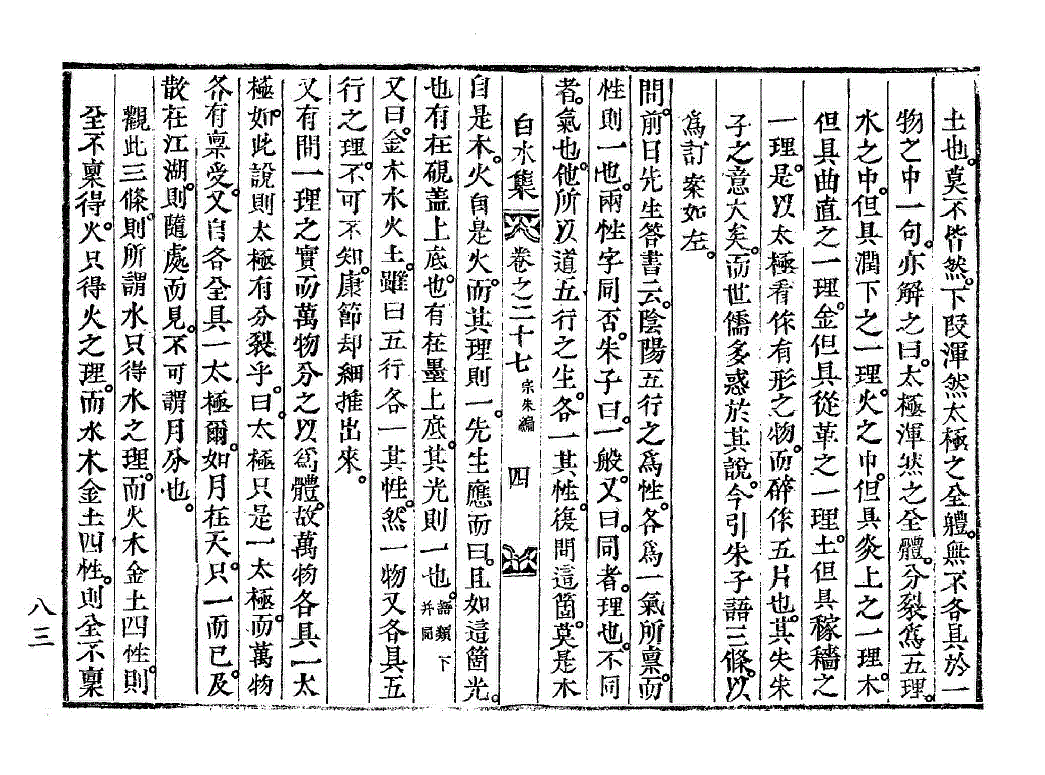 土也。莫不皆然。下段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一句。亦解之曰。太极浑然之全体。分裂为五理。水之中。但具润下之一理。火之中。但具炎上之一理。木但具曲直之一理。金但具从革之一理。土但具稼穑之一理。是以太极看作有形之物。而碎作五片也。其失朱子之意大矣。而世儒多惑于其说。今引朱子语三条。以为订案如左。
土也。莫不皆然。下段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一句。亦解之曰。太极浑然之全体。分裂为五理。水之中。但具润下之一理。火之中。但具炎上之一理。木但具曲直之一理。金但具从革之一理。土但具稼穑之一理。是以太极看作有形之物。而碎作五片也。其失朱子之意大矣。而世儒多惑于其说。今引朱子语三条。以为订案如左。问。前日先生答书云。阴阳五行之为性。各为一气所禀。而性则一也。两性字同否。朱子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气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复问这个。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则一。先生应而曰。且如这个光。也有在砚盖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则一也。(语类下并同)
又曰。金木水火土。虽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节却细推出来。
又有问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太极有分裂乎。曰。太极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
观此三条。则所谓水只得水之理。而火木金土四性。则全不禀得。火只得火之理。而水木金土四性。则全不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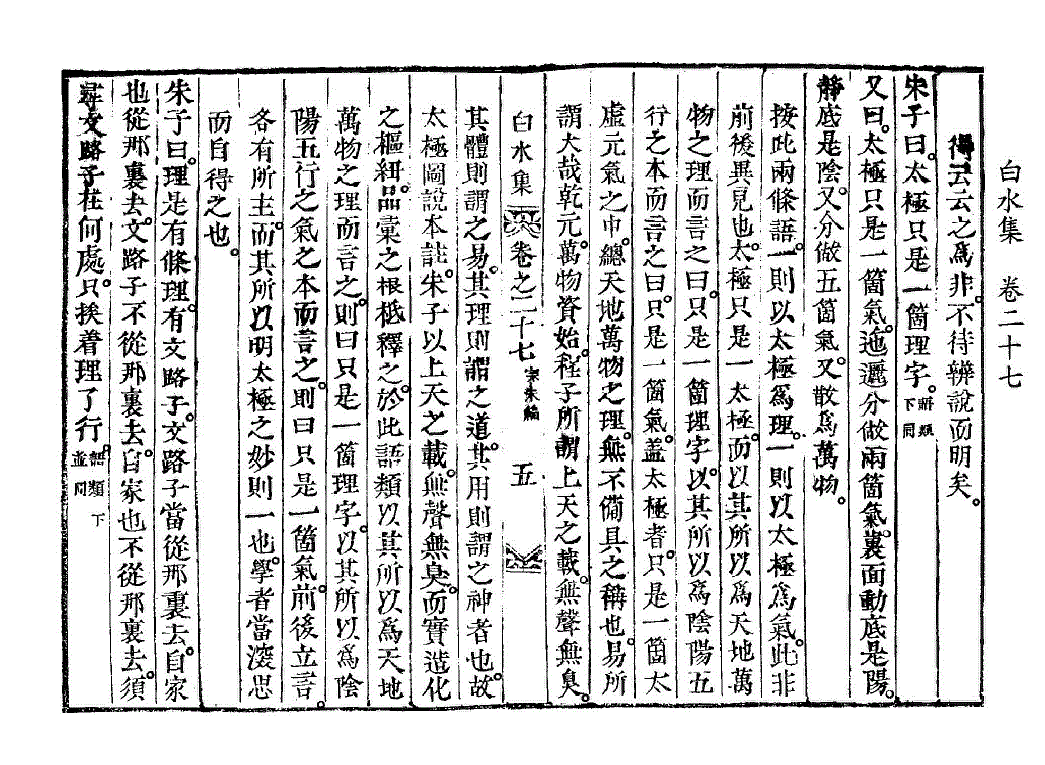 得云云之为非。不待辨说而明矣。
得云云之为非。不待辨说而明矣。朱子曰。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下同)
又曰。太极只是一个气。迤逦分做两个气。里面动底是阳。静底是阴。又分做五个气。又散为万物。
按此两条语。一则以太极为理。一则以太极为气。此非前后异见也。太极只是一太极。而以其所以为天地万物之理而言之曰。只是一个理字。以其所以为阴阳五行之本而言之曰。只是一个气。盖太极者。只是一个太虚元气之中。总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备具之称也。易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程子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者也。故太极图说本注。朱子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释之。于此语类以其所以为天地万物之理而言之。则曰只是一个理字。以其所以为阴阳五行之气之本而言之。则曰只是一个气。前后立言。各有所主。而其所以明太极之妙则一也。学者当深思而自得之也。
朱子曰。理是有条理。有文路子。文路子当从那里去。自家也从那里去。文路子不从那里去。自家也不从那里去。须寻文路子在何处。只挨着理了行。(语类下并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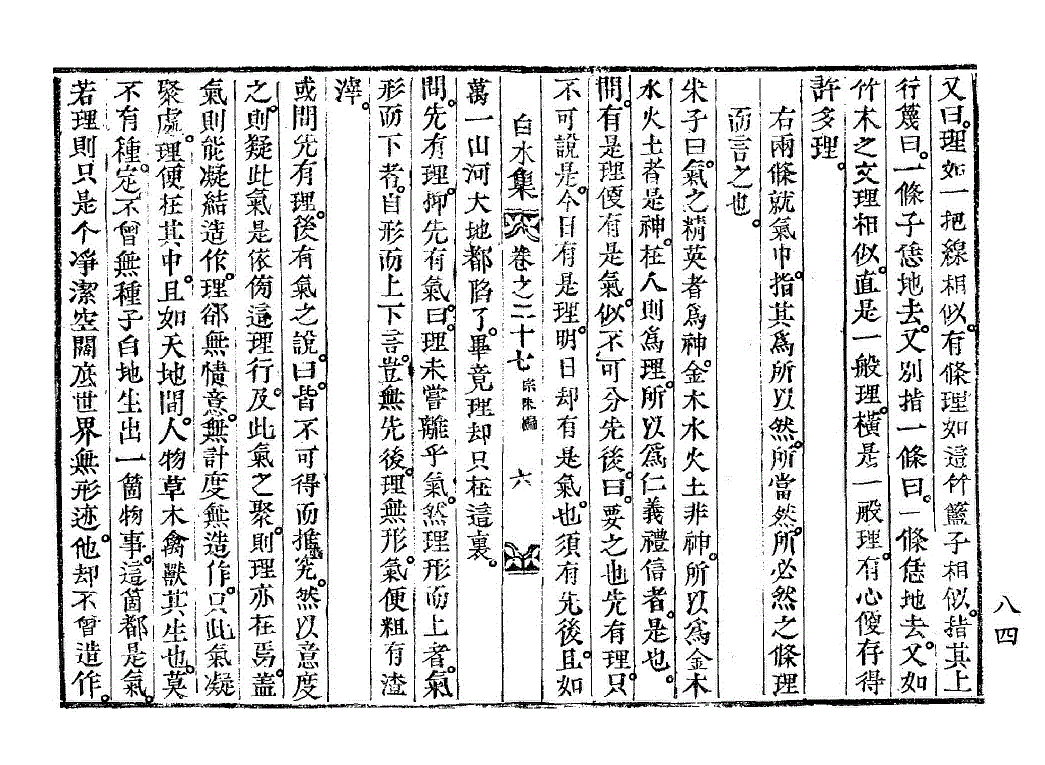 又曰。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如这竹篮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条子恁地去。又别指一条曰。一条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许多理。
又曰。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如这竹篮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条子恁地去。又别指一条曰。一条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许多理。右两条就气中。指其为所以然。所当然。所必然之条理而言之也。
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信者。是也。
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形。气便粗有渣滓。
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曰。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郤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曾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曾造作。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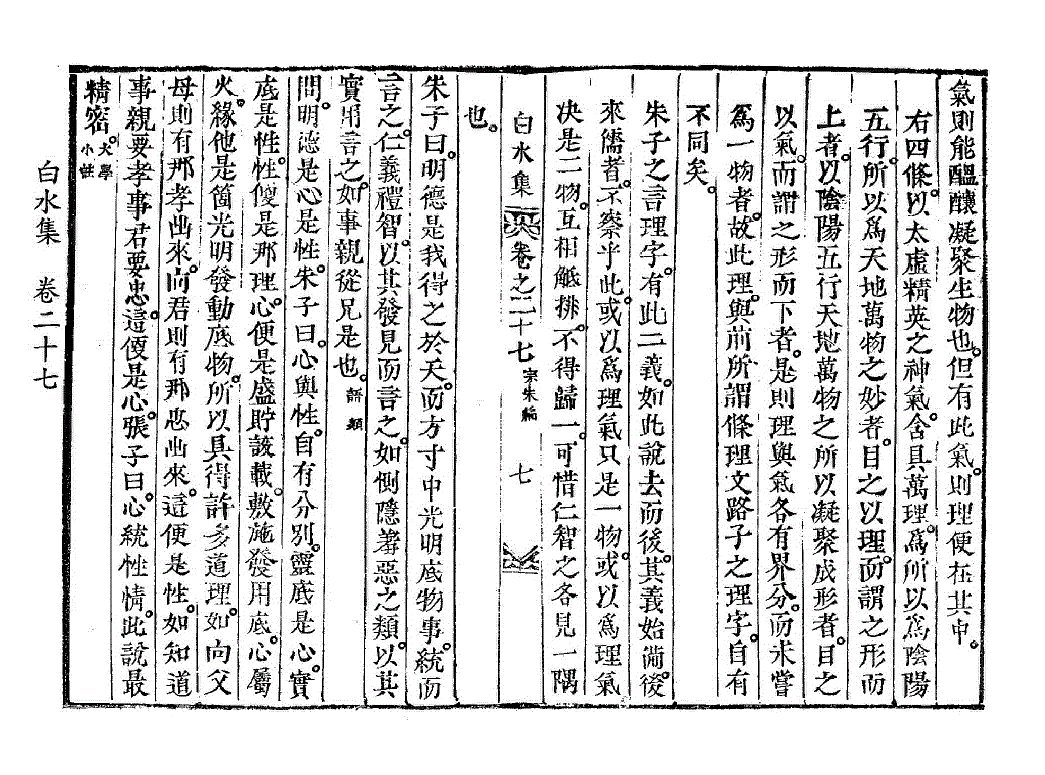 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
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右四条。以太虚精英之神气。含具万理。为所以为阴阳五行。所以为天地万物之妙者。目之以理。而谓之形而上者。以阴阳五行天地万物之所以凝聚成形者。目之以气。而谓之形而下者。是则理与气各有界分。而未尝为一物者。故此理。与前所谓条理文路子之理字。自有不同矣。
朱子之言理字。有此二义。如此说去而后。其义始备。后来儒者。不察乎此。或以为理气只是一物。或以为理气决是二物。互相抵排。不得归一。可惜仁智之各见一隅也。
朱子曰。明德是我得之于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统而言之。仁义礼智。以其发见而言之。如恻隐羞恶之类。以其实用言之。如事亲从兄是也。(语类)
问。明德是心是性。朱子曰。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贮该载。敷施发用底。心属火。缘他是个光明发动底物。所以具得许多道理。如向父母则有那孝出来。向君则有那忠出来。这便是性。如知道事亲要孝事君要忠。这便是心。张子曰。心统性情。此说最精密。(大学小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5L 页
 又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章句)
又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章句)又曰。虚灵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无少欠阙。便是性。随感而动。便是情。(大学小注)
又曰。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语类)
观此数条。则朱子分明以明德为统性情之心。而我东儒者。或以明德看作性则误矣。
朱子曰。心统性情。只就浑然一物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耳。非是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语类)
又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孟子尽心章集注)
又曰。性是理。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
又曰。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语类下同)
又曰。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者也。
观此数条。则可知心之为该理之气。而我东儒者之言。多以为心专是气也。岂不误哉。
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朱子曰。不专是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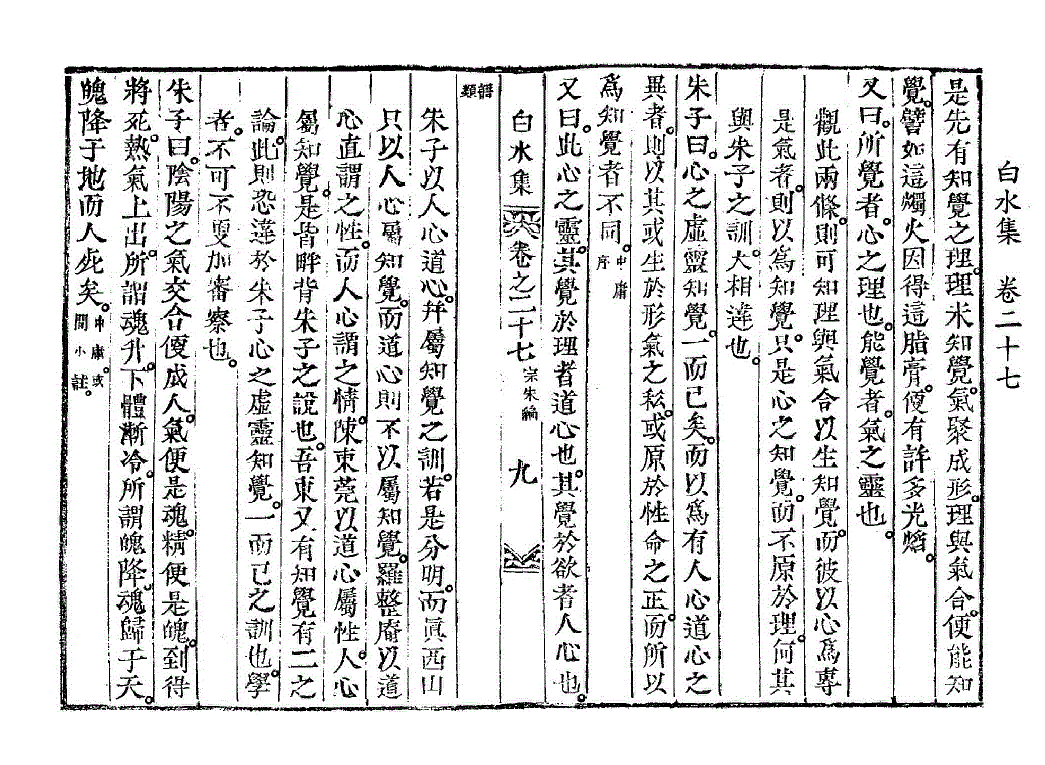 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
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又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
观此两条。则可知理与气合以生知觉。而彼以心为专是气者。则以为知觉。只是心之知觉。而不原于理。何其与朱子之训。大相违也。
朱子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中庸序)
又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语类)
朱子以人心道心。并属知觉之训。若是分明。而真西山只以人心属知觉。而道心则不以属知觉。罗整庵以道心直谓之性。而人心谓之情。陈东莞以道心属性。人心属知觉。是皆畔背朱子之说也。吾东又有知觉有二之论。此则恐违于朱子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之训也。学者。不可不更加审察也。
朱子曰。阴阳之气交合便成人。气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将死。热气上出。所谓魂升。下体渐冷。所谓魄降。魂归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中庸。或问小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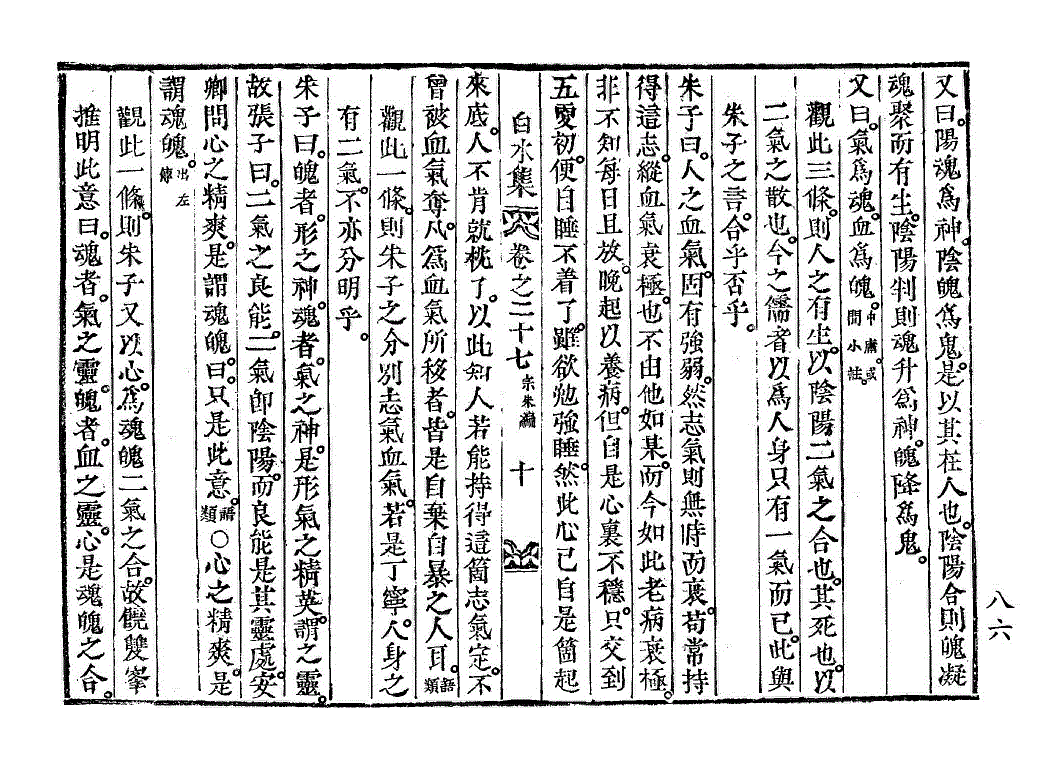 又曰。阳魂为神。阴魄为鬼。是以其在人也。阴阳合则魄凝魂聚而有生。阴阳判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
又曰。阳魂为神。阴魄为鬼。是以其在人也。阴阳合则魄凝魂聚而有生。阴阳判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又曰。气为魂。血为魄。(中庸。或问小注。)
观此三条。则人之有生。以阴阳二气之合也。其死也。以二气之散也。今之儒者以为人身只有一气而已。此与朱子之言。合乎否乎。
朱子曰。人之血气。固有强弱。然志气则无时而衰。苟常持得这志。纵血气衰极。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极。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养病。但自是心里不稳。只交到五更初。便自睡不着了。虽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个起来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这个志气定。不曾被血气夺。凡为血气所移者。皆是自弃自暴之人耳。(语类)
观此一条。则朱子之分别志气血气。若是丁宁。人身之有二气。不亦分明乎。
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是形气之精英。谓之灵。故张子曰。二气之良能。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安卿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曰。只是此意。(语类)○心之精爽。是谓魂魄。(出左传)
观此一条。则朱子又以心。为魂魄二气之合。故饶双峰推明此意曰。魂者。气之灵。魄者。血之灵。心是魂魄之合。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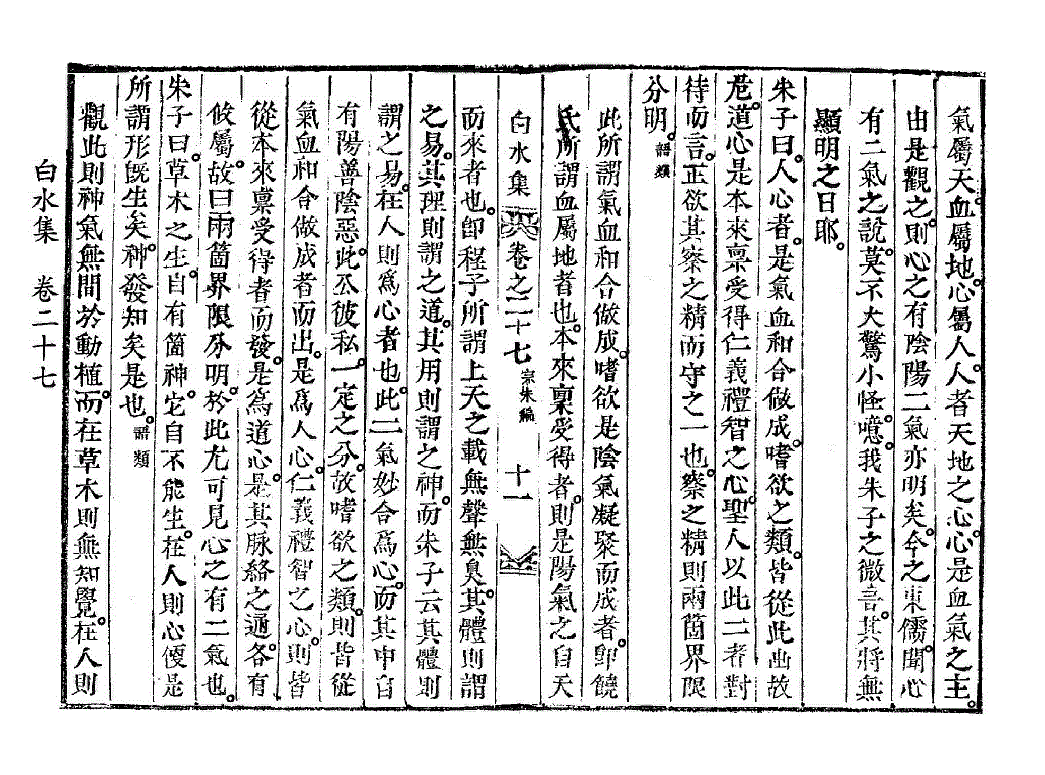 气属天。血属地。心属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气之主。由是观之。则心之有阴阳二气亦明矣。今之东儒。闻心有二气之说。莫不大惊小怪。噫。我朱子之微言。其将无显明之日耶。
气属天。血属地。心属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气之主。由是观之。则心之有阴阳二气亦明矣。今之东儒。闻心有二气之说。莫不大惊小怪。噫。我朱子之微言。其将无显明之日耶。朱子曰。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语类)
此所谓气血和合做成。嗜欲是阴气凝聚而成者。即饶氏所谓血属地者也。本来禀受得者。则是阳气之自天而来者也。即程子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而朱子云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为心者也。此二气妙合为心。而其中自有阳善阴恶。此公彼私。一定之分。故嗜欲之类。则皆从气血和合做成者而出。是为人心。仁义礼智之心。则皆从本来禀受得者而发。是为道心。是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故曰两个界限分明。于此尤可见心之有二气也。
朱子曰。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则心便是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是也。(语类)
观此则神气无间于动植。而在草木则无知觉。在人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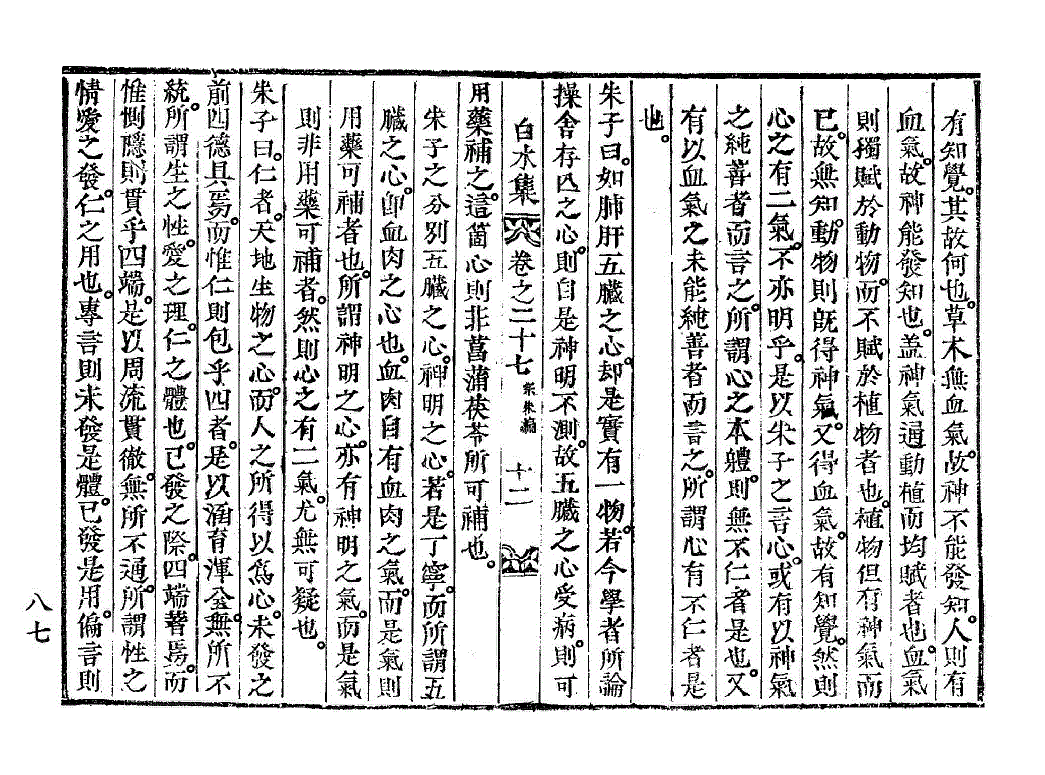 有知觉。其故何也。草木无血气。故神不能发知。人则有血气。故神能发知也。盖神气通动植而均赋者也。血气则独赋于动物。而不赋于植物者也。植物但有神气而已。故无知。动物则既得神气。又得血气。故有知觉。然则心之有二气。不亦明乎。是以朱子之言心。或有以神气之纯善者而言之。所谓心之本体。则无不仁者是也。又有以血气之未能纯善者而言之。所谓心有不仁者是也。
有知觉。其故何也。草木无血气。故神不能发知。人则有血气。故神能发知也。盖神气通动植而均赋者也。血气则独赋于动物。而不赋于植物者也。植物但有神气而已。故无知。动物则既得神气。又得血气。故有知觉。然则心之有二气。不亦明乎。是以朱子之言心。或有以神气之纯善者而言之。所谓心之本体。则无不仁者是也。又有以血气之未能纯善者而言之。所谓心有不仁者是也。朱子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
朱子之分别五脏之心。神明之心。若是丁宁。而所谓五脏之心。即血肉之心也。血肉自有血肉之气。而是气则用药可补者也。所谓神明之心。亦有神明之气。而是气则非用药可补者。然则心之有二气。尤无可疑也。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则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浑全。无所不统。所谓生之性。爱之理。仁之体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而惟恻隐则贯乎四端。是以周流贯彻。无所不通。所谓性之情爱之发。仁之用也。专言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偏言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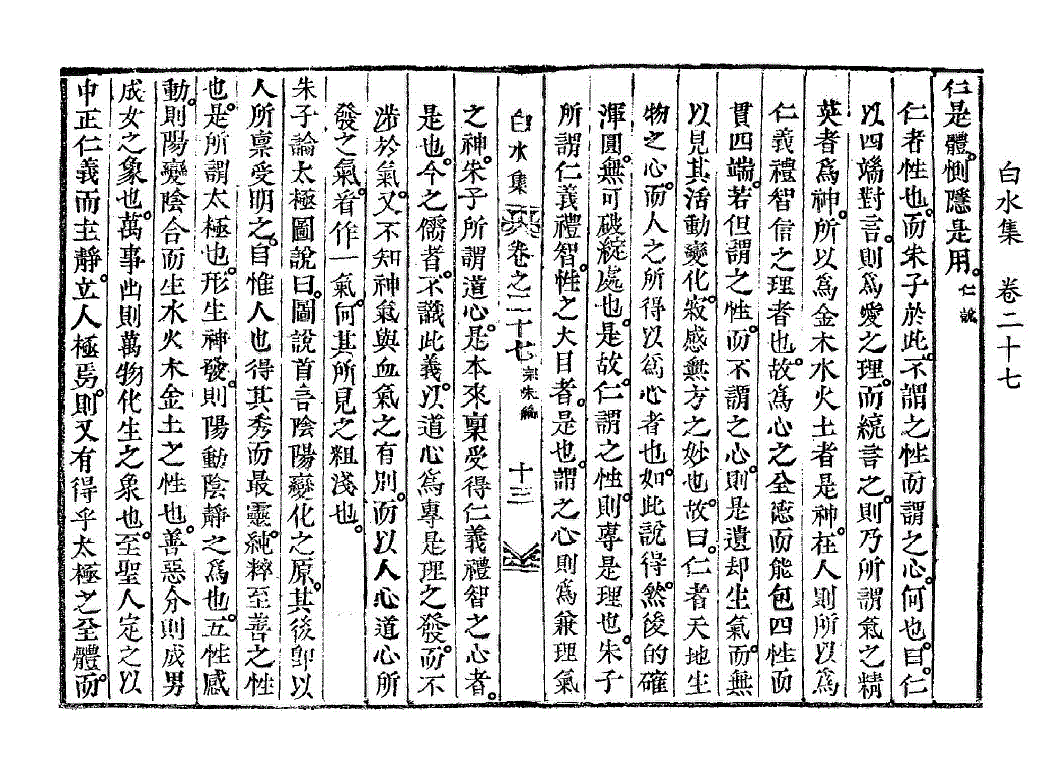 仁是体。恻隐是用。(仁说)
仁是体。恻隐是用。(仁说)仁者性也。而朱子于此。不谓之性而谓之心。何也。曰。仁以四端对言。则为爱之理。而统言之。则乃所谓气之精英者为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所以为仁义礼智信之理者也。故为心之全德而能包四性而贯四端。若但谓之性。而不谓之心。则是遗却生气。而无以见其活动变化。寂感无方之妙也。故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如此说得。然后的确浑圆。无可破绽处也。是故。仁谓之性。则专是理也。朱子所谓仁义礼智。性之大目者。是也。谓之心则为兼理气之神。朱子所谓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者。是也。今之儒者。不识此义。以道心为专是理之发。而不涉于气。又不知神气与血气之有别。而以人心道心所发之气。看作一气。何其所见之粗浅也。
朱子论太极图说曰。图说首言阴阳变化之原。其后即以人所禀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纯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谓太极也。形生神发。则阳动阴静之为也。五性感动。则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恶分则成男成女之象也。万事出则万物化生之象也。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则又有得乎太极之全体。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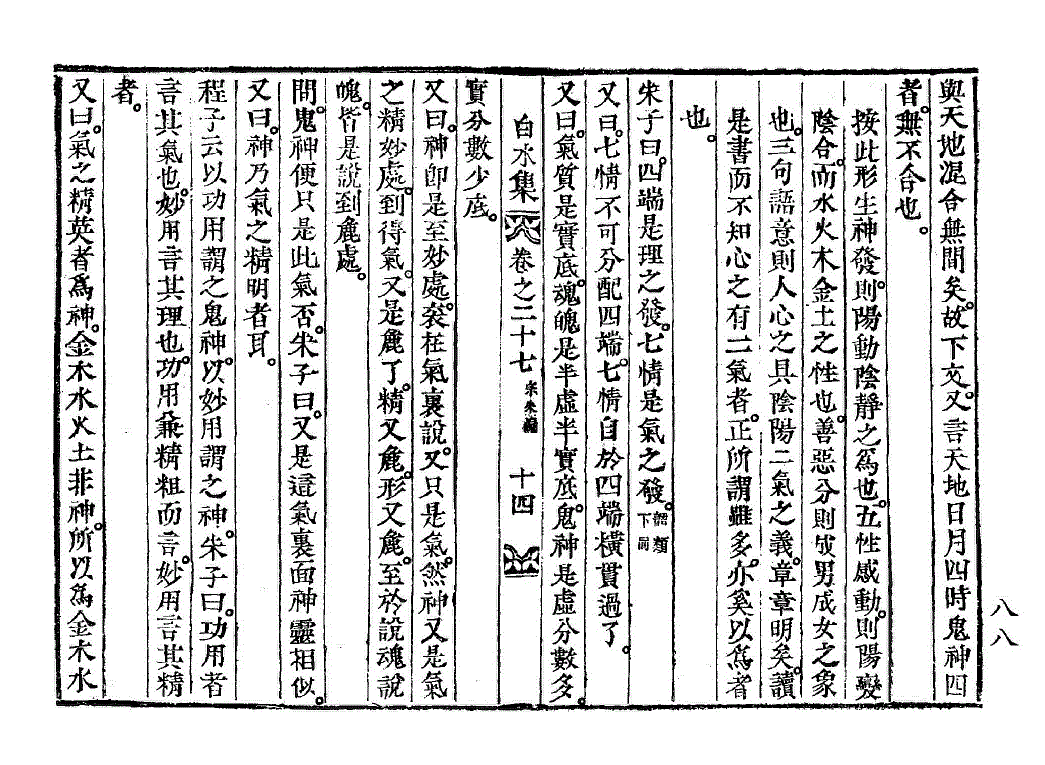 与天地混合无间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四者。无不合也。
与天地混合无间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四者。无不合也。按此形生神发。则阳动阴静之为也。五性感动。则阳变阴合。而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恶分则成男成女之象也。三句语意则人心之具阴阳二气之义。章章明矣。读是书而不知心之有二气者。正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朱子曰。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语类下同)
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
又曰。气质是实底。魂魄是半虚半实底。鬼神是虚分数多。实分数少底。
又曰。神即是至妙处。衮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
问。鬼神便只是此气否。朱子曰。又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
又曰。神乃气之精明者耳。
程子云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朱子曰。功用者言其气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又曰。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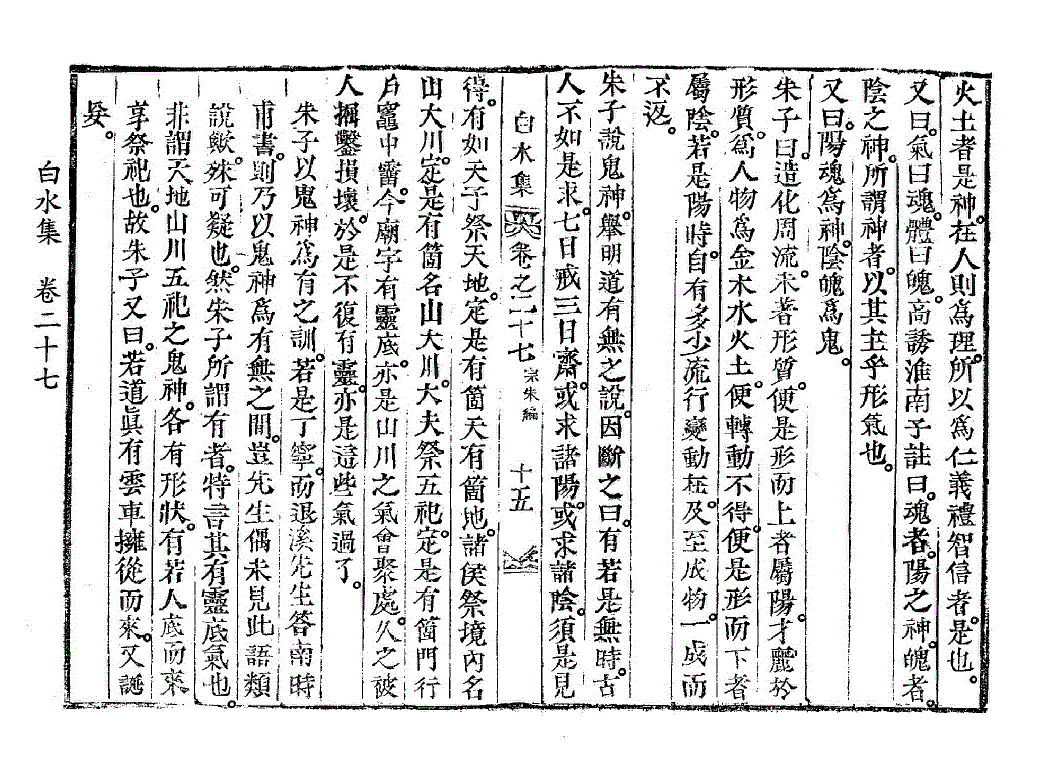 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又曰。气曰魂。体曰魄。高诱淮南子注曰。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
又曰。阳魂为神。阴魄为鬼。
朱子曰。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
朱子说鬼神。举明道有无之说。因断之曰。有若是无时。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斋。或求诸阳。或求诸阴。须是见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个天有个地。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个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个门行户灶中霤。今庙宇有灵底。亦是山川之气会聚处。久之被人掘凿损坏。于是不复有灵。亦是这些气过了。
朱子以鬼神为有之训。若是丁宁。而退溪先生答南时甫书。则乃以鬼神为有无之间。岂先生偶未见此语类说欤。殊可疑也。然朱子所谓有者。特言其有灵底气也。非谓天地山川五祀之鬼神。各有形状。有若人底而来享祭祀也。故朱子又曰。若道真有云车拥从而来。又诞妄。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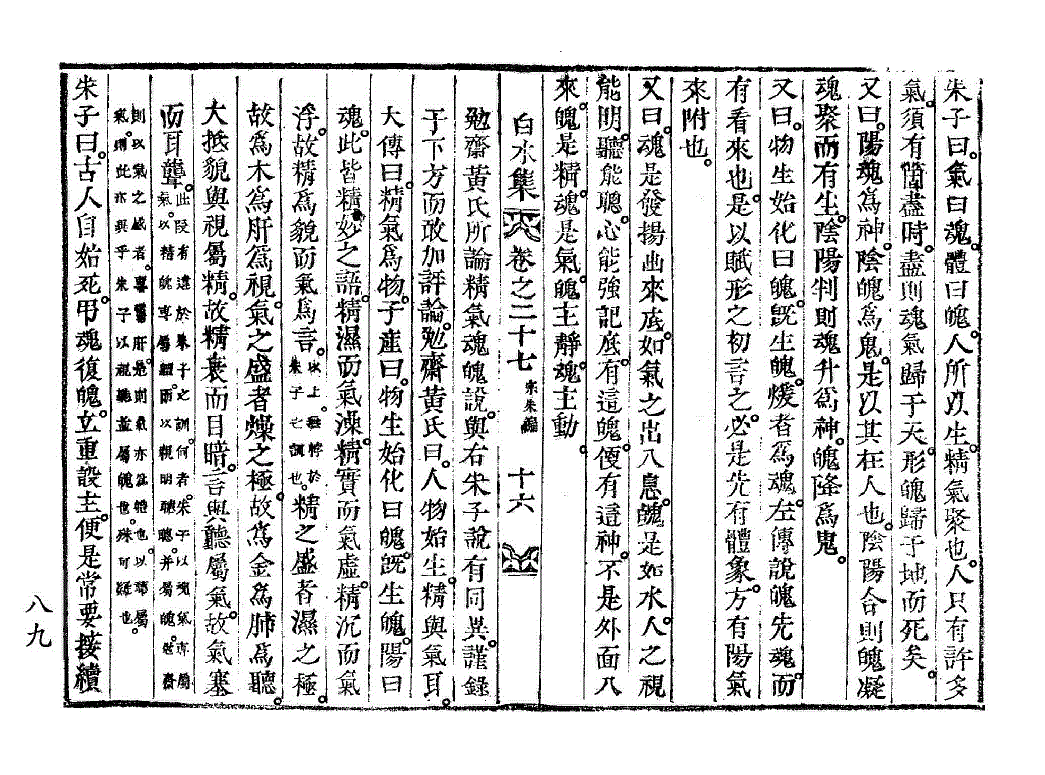 朱子曰。气曰魂。体曰魄。人所以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
朱子曰。气曰魂。体曰魄。人所以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又曰。阳魂为神。阴魄为鬼。是以其在人也。阴阳合则魄凝魂聚而有生。阴阳判则魂升为神。魄降为鬼。
又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为魂。左传说魄先魂。而有看来也。是以赋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体象。方有阳气来附也。
又曰。魂是发扬出来底。如气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视能明。听能聪。心能强记底。有这魄。便有这神。不是外面入来。魄是精。魂是气。魄主静。魂主动。
勉斋黄氏所论精气魂魄说。与右朱子说有同异。谨录于下方而敢加评论。勉斋黄氏曰。人物始生。精与气耳。大传曰。精气为物。子产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此皆精妙之语。精湿而气澡。精实而气虚。精沉而气浮。故精为貌而气为言。(以上。无悖于朱子之训也。)精之盛者湿之极。故为木为肝为视。气之盛者燥之极。故为金为肺为听。大抵貌与视属精。故精衰而目暗。言与听属气。故气塞而耳聋。(此段有违于朱子之训。何者。朱子以魂气专属气。以精魄专属体。而以视明听聪。并属魄。勉斋则以气之盛者。专属肝。是则气亦为体也。以听属气。则此亦异乎朱子以视听并属魄也。殊可疑也。)
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复魄。立重设主。便是常要接续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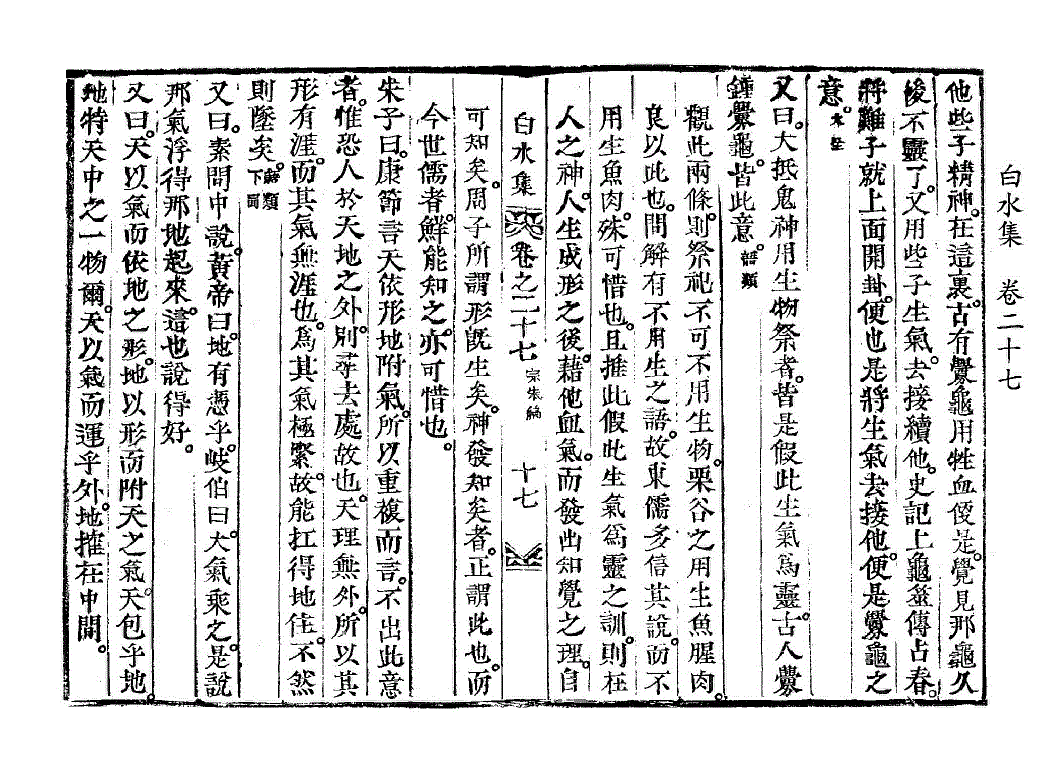 他些子精神。在这里。古有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史记上龟筮传占春。将鸡子就上面开卦。便也是将生气去接他。便是衅龟之意。(大全)
他些子精神。在这里。古有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史记上龟筮传占春。将鸡子就上面开卦。便也是将生气去接他。便是衅龟之意。(大全)又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语类)
观此两条。则祭祀不可不用生物。栗谷之用生鱼腥肉。良以此也。问解有不用生之语。故东儒多信其说。而不用生鱼肉。殊可惜也。且推此假此生气为灵之训。则在人之神。人生成形之后。藉他血气。而发出知觉之理。自可知矣。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者。正谓此也。而今世儒者。鲜能知之。亦可惜也。
朱子曰。康节言天依形地附气。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故也。天理无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气无涯也。为其气极紧。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则坠矣。(语类下同)
又曰。素问中说。黄帝曰。地有凭乎。岐伯曰。大气乘之。是说那气浮得那地起来。这也说得好。
又曰。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地搉在中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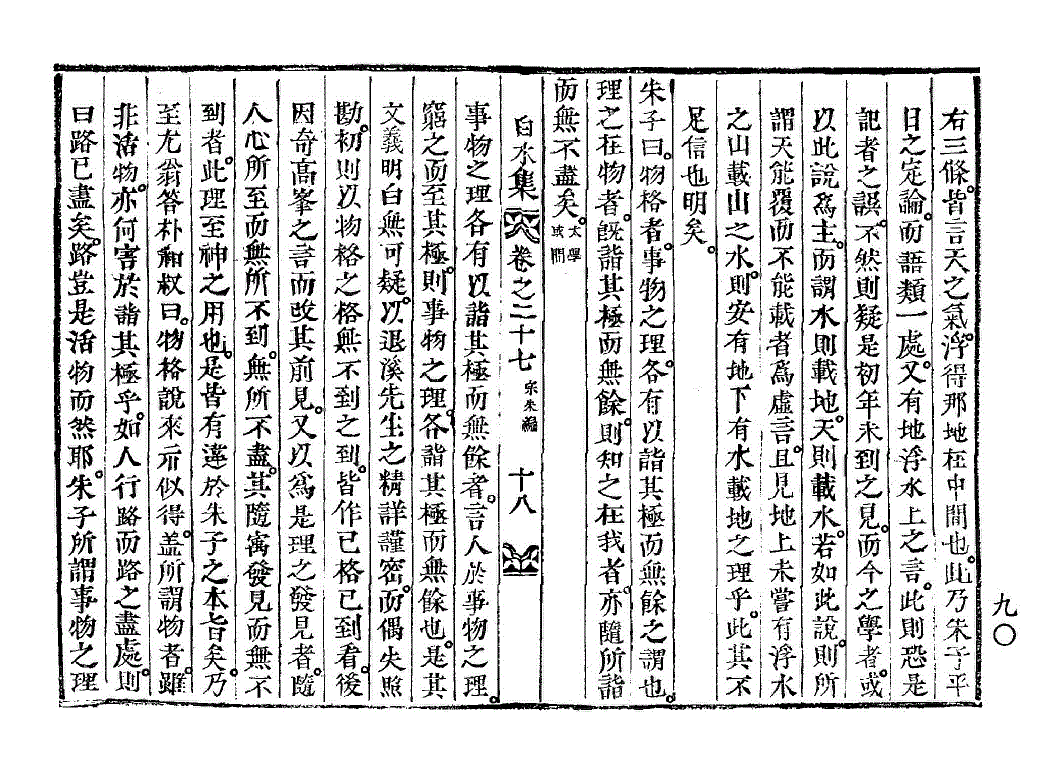 右三条。皆言天之气。浮得那地在中间也。此乃朱子平日之定论。而语类一处。又有地浮水上之言。此则恐是记者之误。不然则疑是初年未到之见。而今之学者。或以此说为主。而谓水则载地。天则载水。若如此说。则所谓天能覆而不能载者为虚言。且见地上未尝有浮水之山载山之水。则安有地下有水载地之理乎。此其不足信也明矣。
右三条。皆言天之气。浮得那地在中间也。此乃朱子平日之定论。而语类一处。又有地浮水上之言。此则恐是记者之误。不然则疑是初年未到之见。而今之学者。或以此说为主。而谓水则载地。天则载水。若如此说。则所谓天能覆而不能载者为虚言。且见地上未尝有浮水之山载山之水。则安有地下有水载地之理乎。此其不足信也明矣。朱子曰。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馀。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太学或问)
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馀者。言人于事物之理。穷之而至其极。则事物之理。各诣其极而无馀也。是其文义明白无可疑。以退溪先生之精详谨密。而偶失照勘。初则以物格之格无不到之到。皆作已格已到看。后因奇高峰之言而改其前见。又以为是理之发见者。随人心所至而无所不到。无所不尽。其随宇(一作寓)发见而无不到者。此理至神之用也。是皆有违于朱子之本旨矣。乃至尤翁答朴和叔曰。物格说来示似得。盖所谓物者。虽非活物。亦何害于诣其极乎。如人行路而路之尽处。则曰路已尽矣。路岂是活物而然耶。朱子所谓事物之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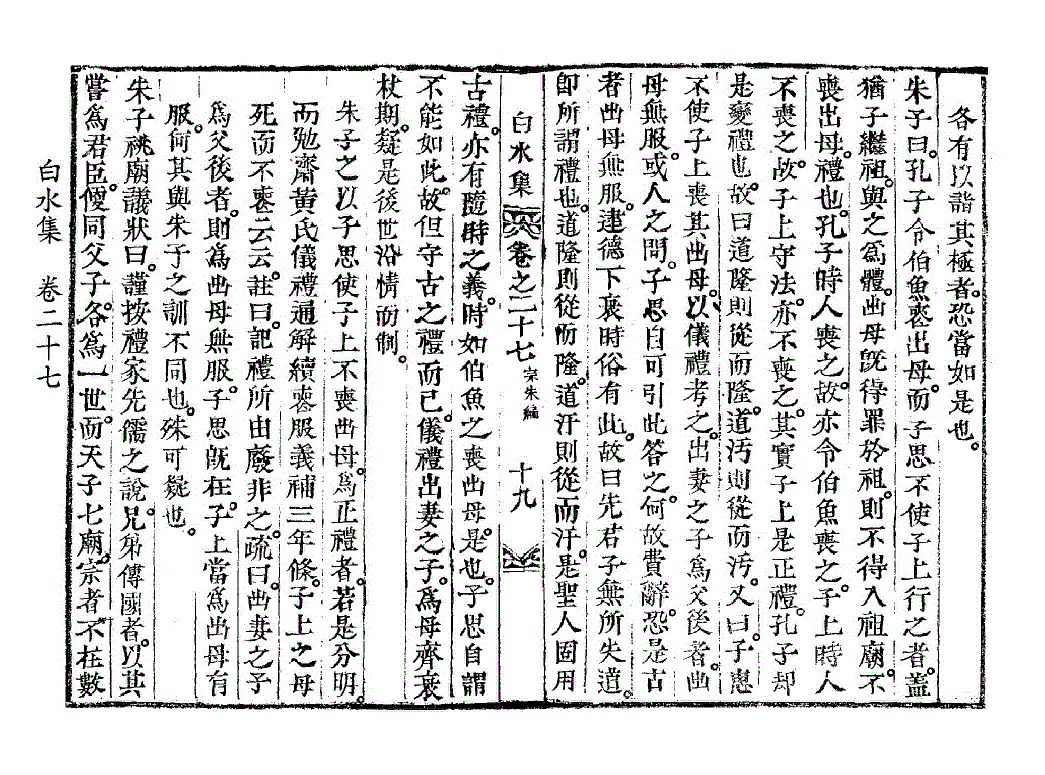 各有以诣其极者。恐当如是也。
各有以诣其极者。恐当如是也。朱子曰。孔子令伯鱼丧出母。而子思不使子上行之者。盖犹子继祖。与之为体。出母既得罪于祖。则不得入祖庙。不丧出母。礼也。孔子时人丧之。故亦令伯鱼丧之。子上时人不丧之。故子上守法。亦不丧之。其实子上是正礼。孔子却是变礼也。故曰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又曰。子思不使子上丧其出母。以仪礼考之。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出母无服。或人之问。子思自可引此答之。何故费辞。恐是古者出母无服。逮德下衰时俗有此。故曰先君子无所失道。即所谓礼也。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是圣人固用古礼。亦有随时之义。时如伯鱼之丧出母。是也。子思自谓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礼而已。仪礼出妻之子。为母齐衰杖期。疑是后世沿情而制。
朱子之以子思使子上不丧出母。为正礼者。若是分明。而勉斋黄氏仪礼通解续丧服义补三年条。子上之母死而不丧云云。注曰。记礼所由废非之。疏曰。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子思既在。子上当为出母有服。何其与朱子之训不同也。殊可疑也。
朱子祧庙议状曰。谨按礼家先儒之说。兄弟传国者。以其尝为君臣。便同父子。各为一世。而天子七庙。宗者不在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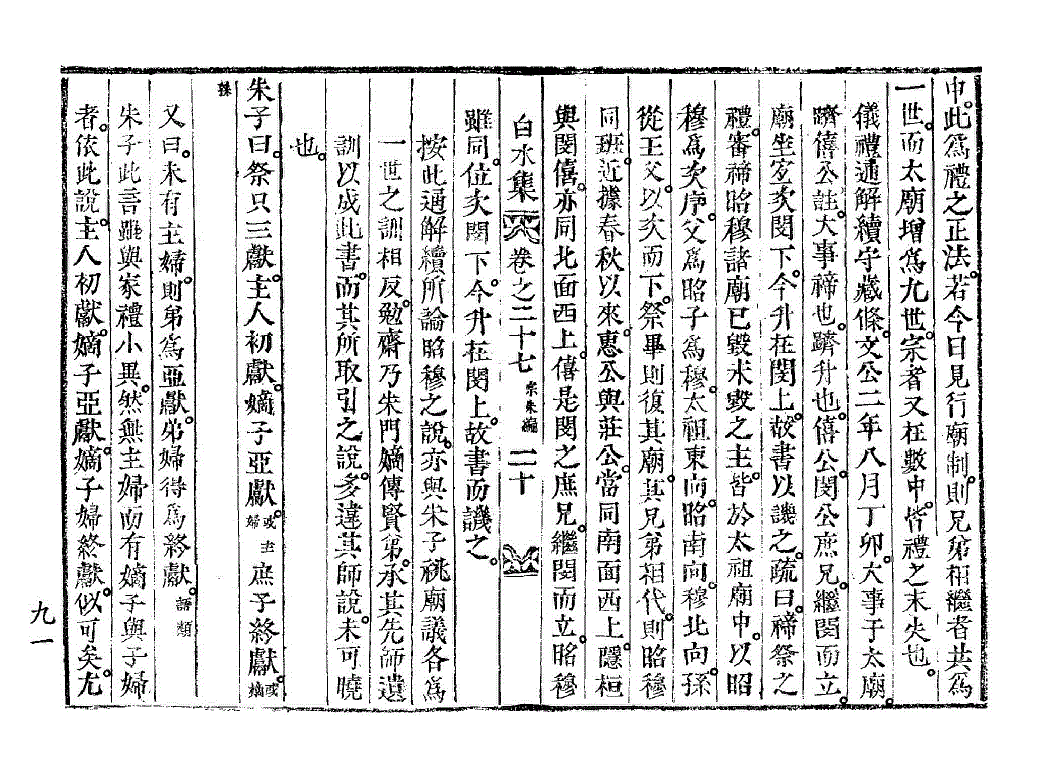 中。此为礼之正法。若今日见行庙制。则兄弟相继者共为一世。而太庙增为九世。宗者又在数中。皆礼之末失也。
中。此为礼之正法。若今日见行庙制。则兄弟相继者共为一世。而太庙增为九世。宗者又在数中。皆礼之末失也。仪礼通解续守藏条。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注。大事禘也。跻升也。僖公。闵公庶兄。继闵而立。庙坐宜次闵下。今升在闵上。故书以讥之。疏曰。禘祭之礼。审禘昭穆诸庙已毁未毁之主。皆于太祖庙中。以昭穆为次序。父为昭子为穆。太祖东向。昭南向。穆北向。孙从王父。以次而下。祭毕则复其庙。其兄弟相代。则昭穆同班。近据春秋以来。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闵之庶兄。继闵而立。昭穆虽同。位次闵下。今升在闵上。故书而讥之。
按此通解续所论昭穆之说。亦与朱子祧庙议各为一世之训相反。勉斋乃朱门嫡传贤弟。承其先师遗训以成此书。而其所取引之说。多违其师说。未可晓也。
朱子曰。祭只三献。主人初献。嫡子亚献。(或主妇)庶子终献。(或嫡孙)
又曰。未有主妇。则弟为亚献。弟妇得为终献。(语类)
朱子此言虽与家礼小异。然无主妇而有嫡子与子妇者。依此说。主人初献。嫡子亚献。嫡子妇终献。似可矣。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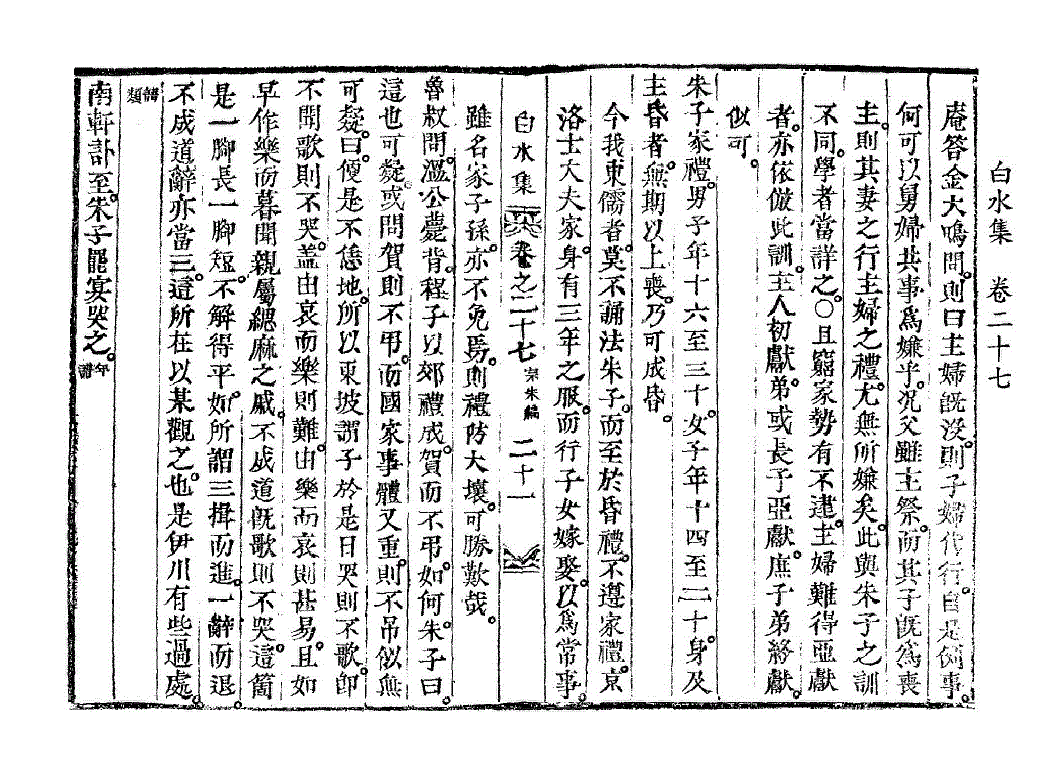 庵答金大鸣问。则曰主妇既没。则子妇代行。自是例事。何可以舅妇共事为嫌乎。况父虽主祭。而其子既为丧主。则其妻之行主妇之礼。尤无所嫌矣。此与朱子之训不同。学者当详之。○且穷家势有不逮。主妇难得亚献者。亦依仿此训。主人初献。弟或长子亚献。庶子弟终献。似可。
庵答金大鸣问。则曰主妇既没。则子妇代行。自是例事。何可以舅妇共事为嫌乎。况父虽主祭。而其子既为丧主。则其妻之行主妇之礼。尤无所嫌矣。此与朱子之训不同。学者当详之。○且穷家势有不逮。主妇难得亚献者。亦依仿此训。主人初献。弟或长子亚献。庶子弟终献。似可。朱子家礼。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无期以上丧。乃可成昏。
今我东儒者。莫不诵法朱子。而至于昏礼。不遵家礼。京洛士大夫家。身有三年之服。而行子女嫁娶。以为常事。虽名家子孙。亦不免焉。则礼防大坏。可胜叹哉。
鲁叔问。温公薨背。程子以郊礼成。贺而不吊。如何。朱子曰。这也可疑。或问贺则不吊。而国家事体又重。则不吊似无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东坡谓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闻歌则不哭。盖由哀而乐则难。由乐而哀则甚易。且如早作乐而暮闻亲属缌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则不哭。这个是一脚长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谓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不成道辞亦当三。这所在以某观之。也是伊川有些过处。(语类)
南轩讣至。朱子罢宴哭之。(年谱)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2L 页
 朱子尝书戒子云。比见墓祭土神之礼。全然灭裂。吾甚惧焉。既为先公托体山林而祀其主者。岂可如此。今后可与墓前一样。菜果鲊脯饭茶汤各一器。以尽吾宁亲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杀。
朱子尝书戒子云。比见墓祭土神之礼。全然灭裂。吾甚惧焉。既为先公托体山林而祀其主者。岂可如此。今后可与墓前一样。菜果鲊脯饭茶汤各一器。以尽吾宁亲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杀。此是朱子教人之至意。今世之人。不识此道理。其祭山神。馔品降杀于墓祭者多。行礼之家。所当深戒也。
家礼忌日设位。注云止设一位。
由是观之。则朱子于忌日。未尝并祭考妣。而我 朝先贤率皆并祭。此恐是宁失于厚之意。而窃观人家或有再娶三娶者。其子孙行并祭之日。若各设位卓。则三四位三四卓。不可容于一间堂室之中。若只设一椅而并奉三四神主。只设一分馔而并祭三四位。则又不成道理。且三四代许多忌日。并祭考妣而逐位供一分馔。则决非贫穷子孙所可堪当。此终是行不得之事也。莫如一遵朱子家礼而行之。则既不失于礼之正。又为永久无弊之道也。
先生家凡值远讳。早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献之礼。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则以待宾客。(语类)
应秀行忌祀之日。有宾客则从俗以祭祀食物待之。而未知其合礼与否。心常持疑。今见此语类。然后始知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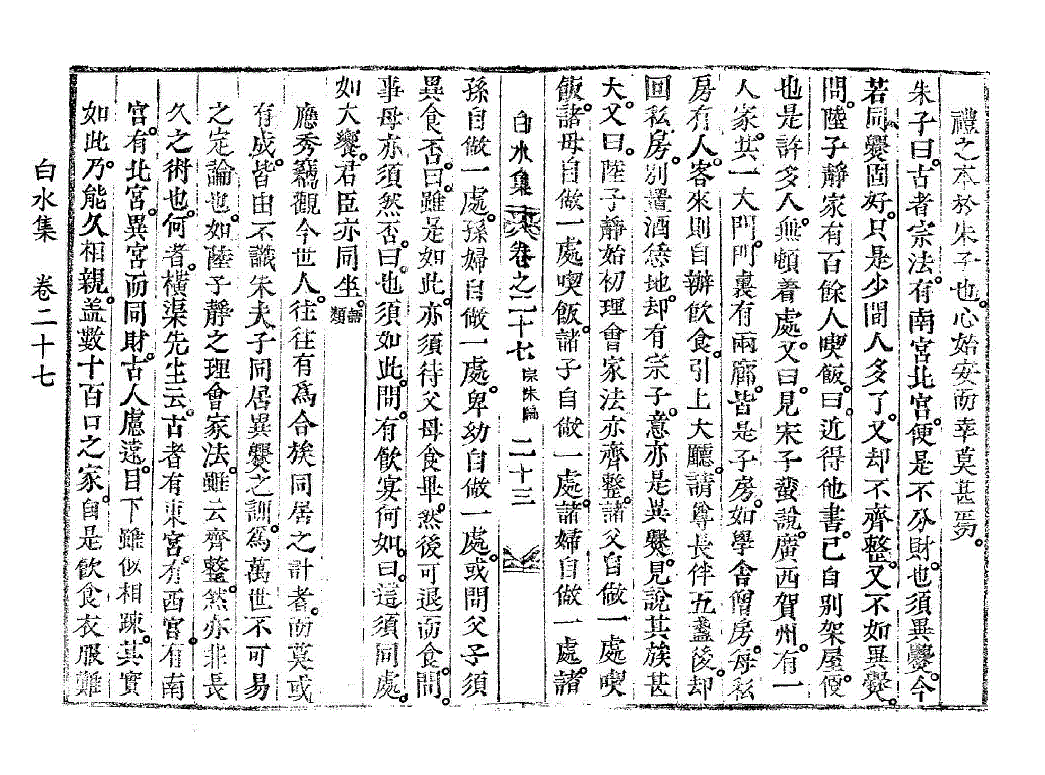 礼之本于朱子也。心始安而幸莫甚焉。
礼之本于朱子也。心始安而幸莫甚焉。朱子曰。古者宗法。有南宫北宫。便是不分财。也须异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间人多了。又却不齐整。又不如异爨。
问。陆子静家有百馀人吃饭。曰。近得他书。已自别架屋。便也是许多人。无顿着处。又曰。见宋子蜚说。广西贺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门。门里有两廊。皆是子房。如学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来则自办饮食。引上大厅。请尊长伴五盏后。却回私房。别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异爨。见说其族甚大。又曰。陆子静始初理会家法亦齐整。诸父自做一处吃饭。诸母自做一处吃饭。诸子自做一处。诸妇自做一处。诸孙自做一处。孙妇自做一处。卑幼自做一处。或问父子须异食否。曰。虽是如此。亦须待父母食毕。然后可退而食。问。事母亦须然否。曰。也须如此。问。有饮宴何如。曰。这须同处。如大飨。君臣亦同坐。(语类)
应秀窃观今世人。往往有为合族同居之计者。而莫或有成。皆由不识朱夫子同居异爨之训。为万世不可易之定论也。如陆子静之理会家法。虽云齐整。然亦非长久之术也。何者。横渠先生云。古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宫而同财。古人虑远。目下虽似相疏。其实如此。乃能久相亲。盖数十百口之家。自是饮食衣服难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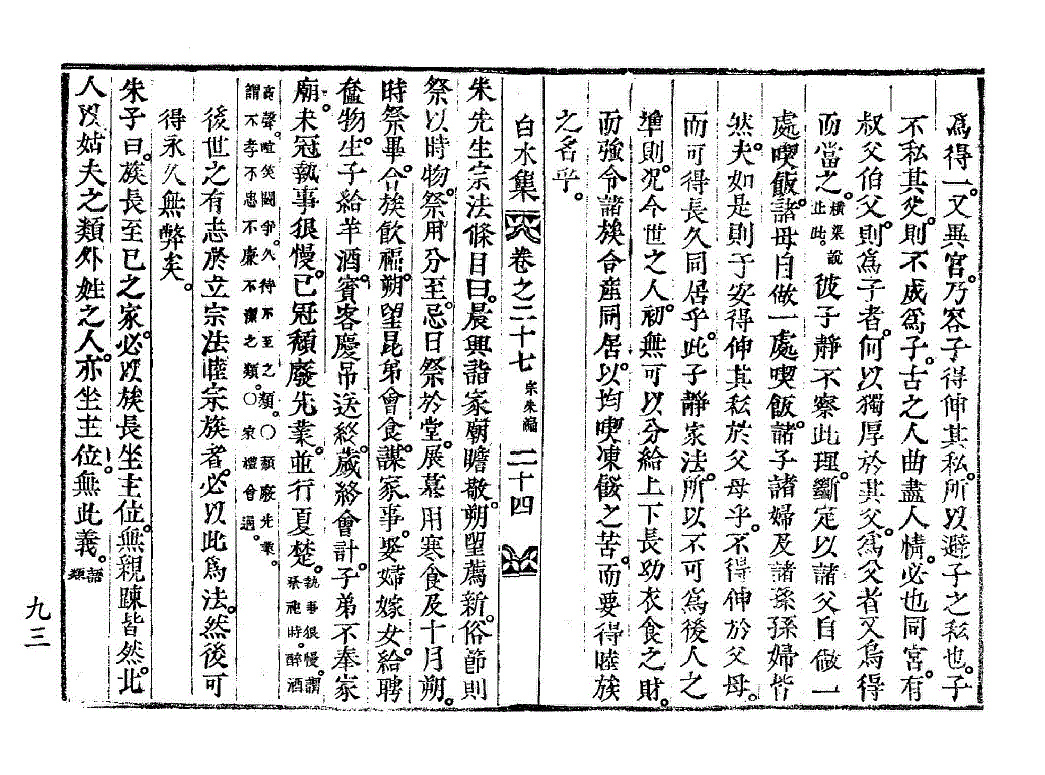 为得一。又异宫。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古之人曲尽人情。必也同宫。有叔父伯父。则为子者。何以独厚于其父。为父者又乌得而当之。(横渠说止此。)彼子静不察此理。断定以诸父自做一处吃饭。诸母自做一处吃饭。诸子诸妇及诸孙孙妇皆然。夫如是则子安得伸其私于父母乎。不得伸于父母。而可得长久同居乎。此子静家法。所以不可为后人之准则。况今世之人。初无可以分给上下长幼衣食之财。而强令诸族合产同居。以均吃冻馁之苦。而要得睦族之名乎。
为得一。又异宫。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古之人曲尽人情。必也同宫。有叔父伯父。则为子者。何以独厚于其父。为父者又乌得而当之。(横渠说止此。)彼子静不察此理。断定以诸父自做一处吃饭。诸母自做一处吃饭。诸子诸妇及诸孙孙妇皆然。夫如是则子安得伸其私于父母乎。不得伸于父母。而可得长久同居乎。此子静家法。所以不可为后人之准则。况今世之人。初无可以分给上下长幼衣食之财。而强令诸族合产同居。以均吃冻馁之苦。而要得睦族之名乎。朱先生宗法条目曰。晨兴诣家庙瞻敬。朔望荐新。俗节则祭以时物。祭用分至。忌日祭于堂。展墓用寒食及十月朔。时祭毕。合族饮福。朔望昆弟会食。谋家事。娶妇嫁女。给聘奁物。生子给羊酒。宾客庆吊送终。岁终会计。子弟不奉家庙。未冠执事狠慢。已冠颓废先业。并行夏楚。(执事狠慢。谓祭祀时。醉酒高声。喧笑斗争。久待不至之类。○颓废先业。谓不孝不忠不廉不洁之类。○家礼会通。)
后世之有志于立宗法睦宗族者。必以此为法。然后可得永久无弊矣。
朱子曰。族长至己之家。必以族长坐主位。无亲疏皆然。北人以姑夫之类外姓之人。亦坐主位。无此义。(语类)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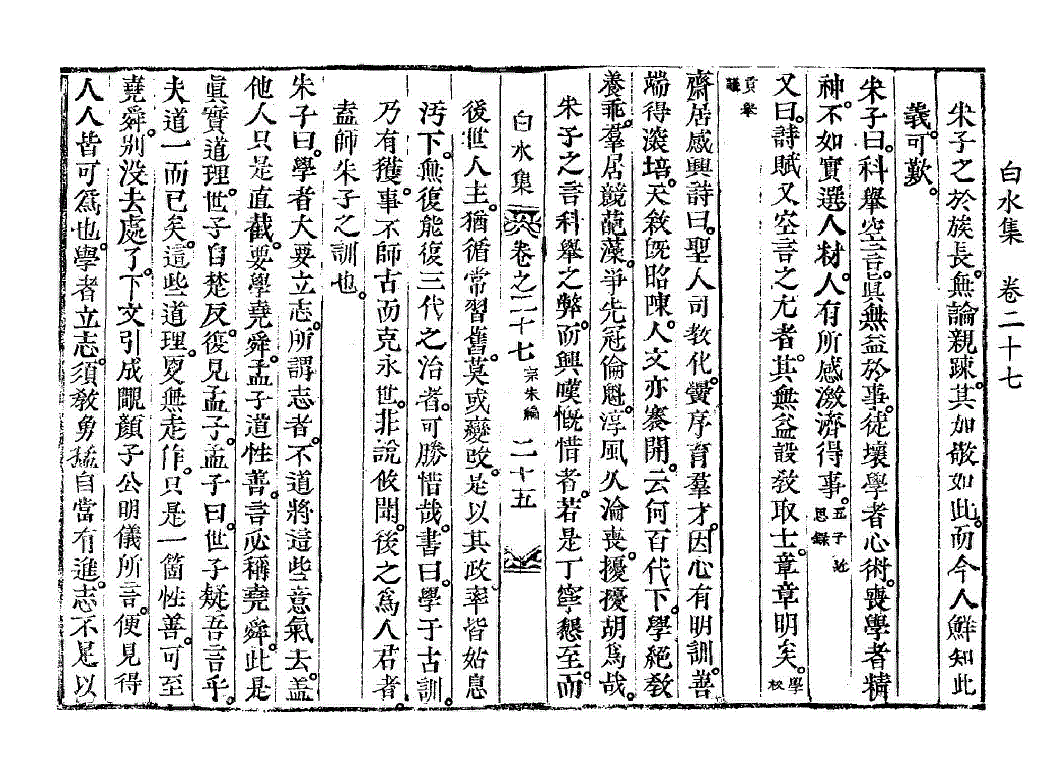 朱子之于族长。无论亲疏。其加敬如此。而今人鲜知此义。可叹。
朱子之于族长。无论亲疏。其加敬如此。而今人鲜知此义。可叹。朱子曰。科举空言。真无益于事。徒坏学者心术。丧学者精神。不如实选人材。人有所感激济得事。(五子近思录)
又曰。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设教取士。章章明矣。(学校贡举议)
斋居感兴诗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才。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久沦丧。扰扰胡为哉。
朱子之言科举之弊。而兴叹慨惜者。若是丁宁恳至。而后世人主。犹循常习旧。莫或变改。是以其政。率皆姑息污下。无复能复三代之治者。可胜惜哉。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而克永世。非说攸闻。后之为人君者。盍师朱子之训也。
朱子曰。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是真实道理。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这些道理。更无走作。只是一个性善。可至尧舜。别没去处了。下文引成覸颜子公明仪所言。便见得人人皆可为也。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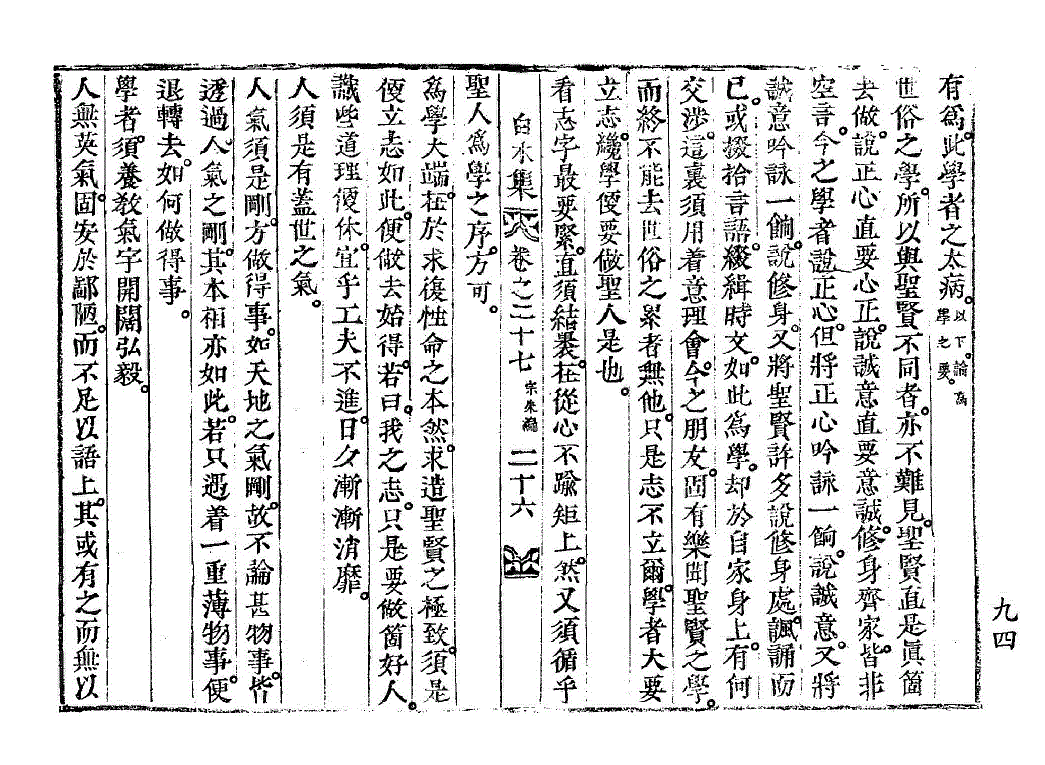 有为。此学者之太病。(以下。论为学之要。)
有为。此学者之太病。(以下。论为学之要。)世俗之学。所以与圣贤不同者。亦不难见。圣贤直是真个去做。说正心直要心正。说诚意直要意诚。修身齐家。皆非空言。今之学者说正心。但将正心吟咏一饷。说诚意。又将诚意吟咏一饷。说修身。又将圣贤许多说修身处。讽诵而已。或掇拾言语。缀缉时文。如此为学。却于自家身上。有何交涉。这里须用着意理会。今之朋友。固有乐闻圣贤之学。而终不能去世俗之累者无他。只是志不立尔。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看志字最要紧。直须结裹。在从心不踰矩上。然又须循乎圣人为学之序。方可。
为学大端。在于求复性命之本然。求造圣贤之极致。须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个好人。识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进。日夕渐渐消靡。
人须是有盖世之气。
人气须是刚。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气刚。故不论甚物事。皆透过。人气之刚。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转去。如何做得事。
学者。须养教气宇开阔弘毅。
人无英气。固安于鄙陋。而不足以语上。其或有之而无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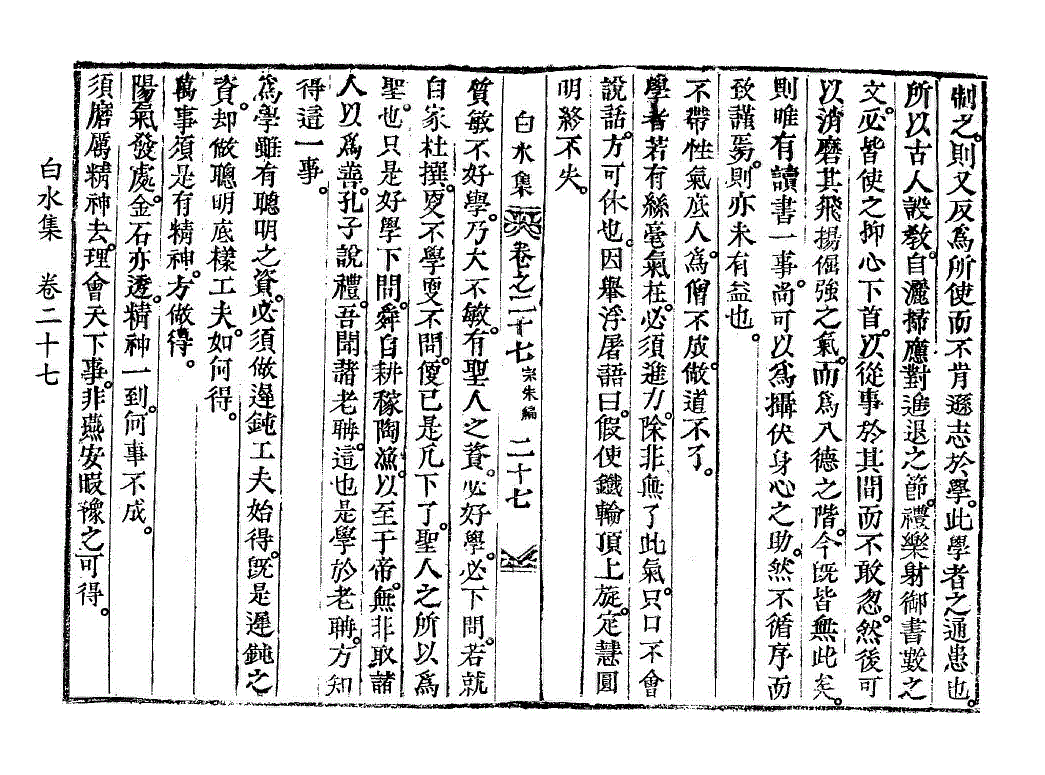 制之。则又反为所使而不肯逊志于学。此学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设教。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而为入德之阶。今既皆无此矣。则唯有读书一事。尚可以为摄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谨焉。则亦未有益也。
制之。则又反为所使而不肯逊志于学。此学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设教。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而为入德之阶。今既皆无此矣。则唯有读书一事。尚可以为摄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谨焉。则亦未有益也。不带性气底人。为僧不成。做道不了。
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进力。除非无了此气。只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因举浮屠语曰。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质敏不好学。乃大不敏。有圣人之资。必好学。必下问。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学更不问。便已是凡下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也只是好学下问。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于帝。无非取诸人以为善。孔子说礼。吾闻诸老聃。这也是学于老聃。方知得这一事。
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
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
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须磨厉精神去。理会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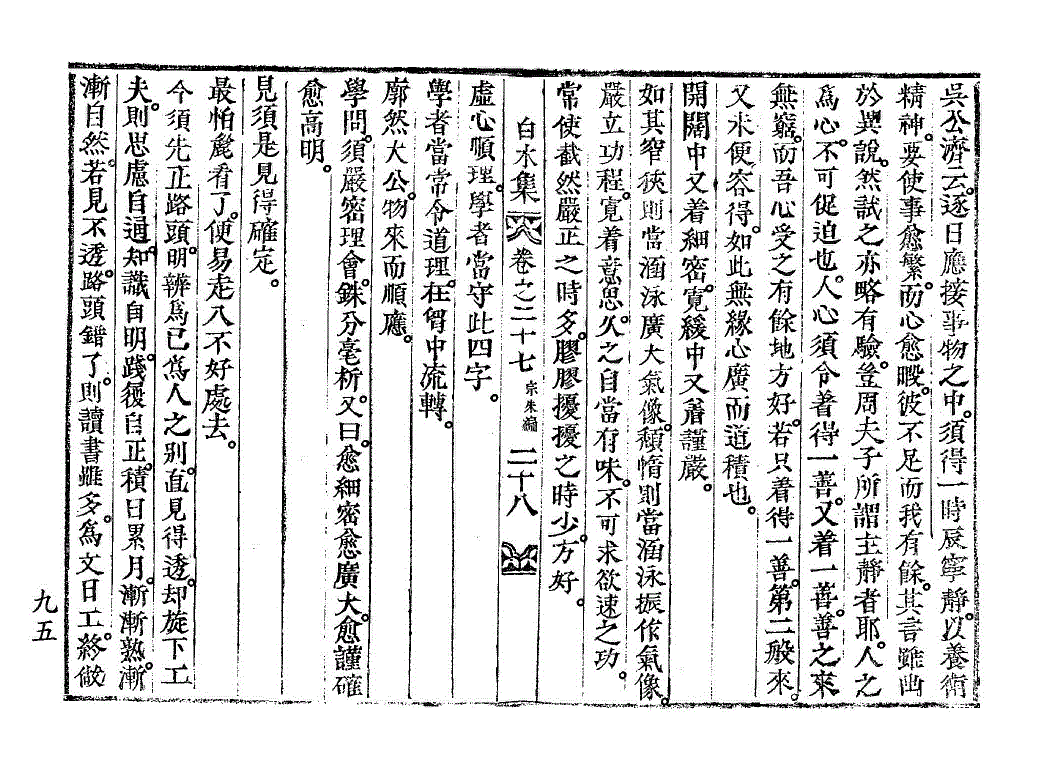 吴公济云。逐日应接事物之中。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馀。其言虽出于异说。然试之亦略有验。岂周夫子所谓主静者耶。人之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须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来无穷。而吾心受之有馀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二般来。又未便容得。如此无缘心广而道积也。
吴公济云。逐日应接事物之中。须得一时辰宁静。以养卫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馀。其言虽出于异说。然试之亦略有验。岂周夫子所谓主静者耶。人之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须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善之来无穷。而吾心受之有馀地方好。若只着得一善。第二般来。又未便容得。如此无缘心广而道积也。开阔中又着细密。宽缓中又着谨严。
如其窄狭则当涵泳广大气像。颓惰则当涵泳振作气像。
严立功程。宽着意思。久之自当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常使截然严正之时多。胶胶扰扰之时少。方好。
虚心顺理。学者当守此四字。
学者当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转。
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
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又曰。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
见须是见得确定。
最怕粗看了。便易走入不好处去。
今须先正路头。明辨为己为人之别。直见得透。却旋下工夫。则思虑自通。知识自明。践履自正。积日累月。渐渐熟。渐渐自然。若见不透。路头错了。则读书虽多。为文日工。终做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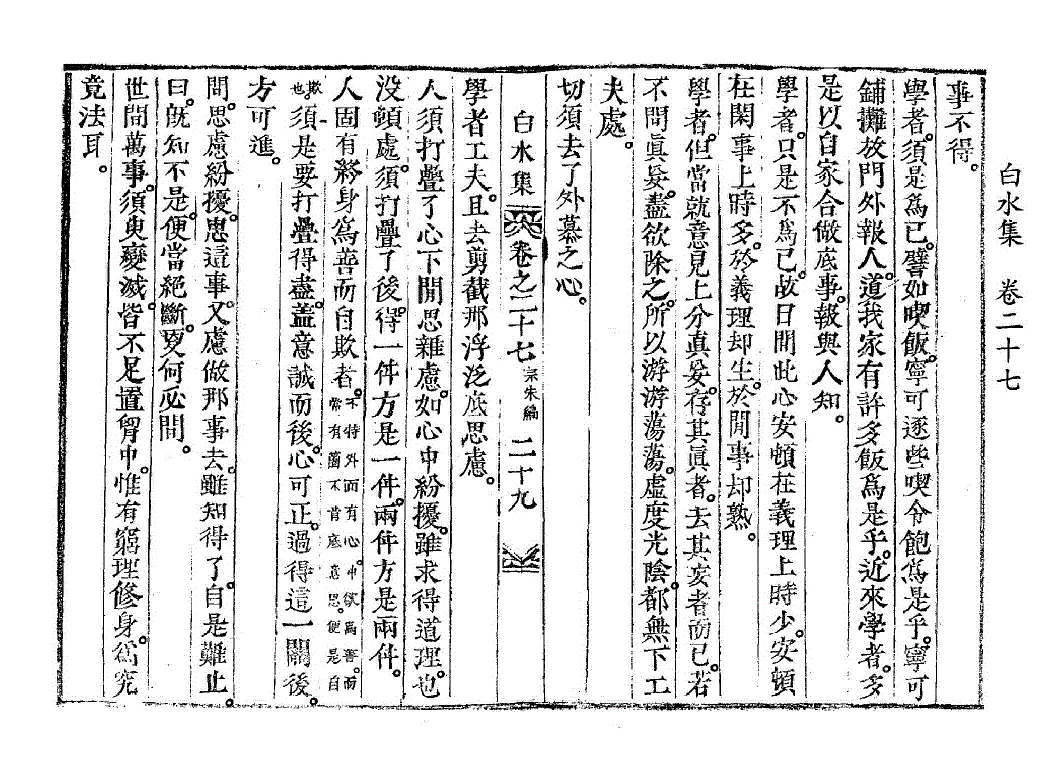 事不得。
事不得。学者。须是为己。譬如吃饭。宁可逐些吃令饱为是乎。宁可铺摊放门外报人。道我家有许多饭为是乎。近来学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报与人知。
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閒事却熟。
学者。但当就意见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问真妄。尽欲除之。所以游游荡荡。虚度光阴。都无下工夫处。
切须去了外慕之心。
学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虑。
人须打叠了心下閒思杂虑。如心中纷扰。虽求得道理。也没顿处。须打叠了后。得一件方是一件。两件方是两件。
人固有终身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而有心。中欲为善。而常有个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须是要打叠得尽。盖意诚而后。心可正。过得这一关后。方可进。
问。思虑纷扰。思这事。又虑做那事去。虽知得了。自是难止。曰。既知不是。便当绝断。更何必问。
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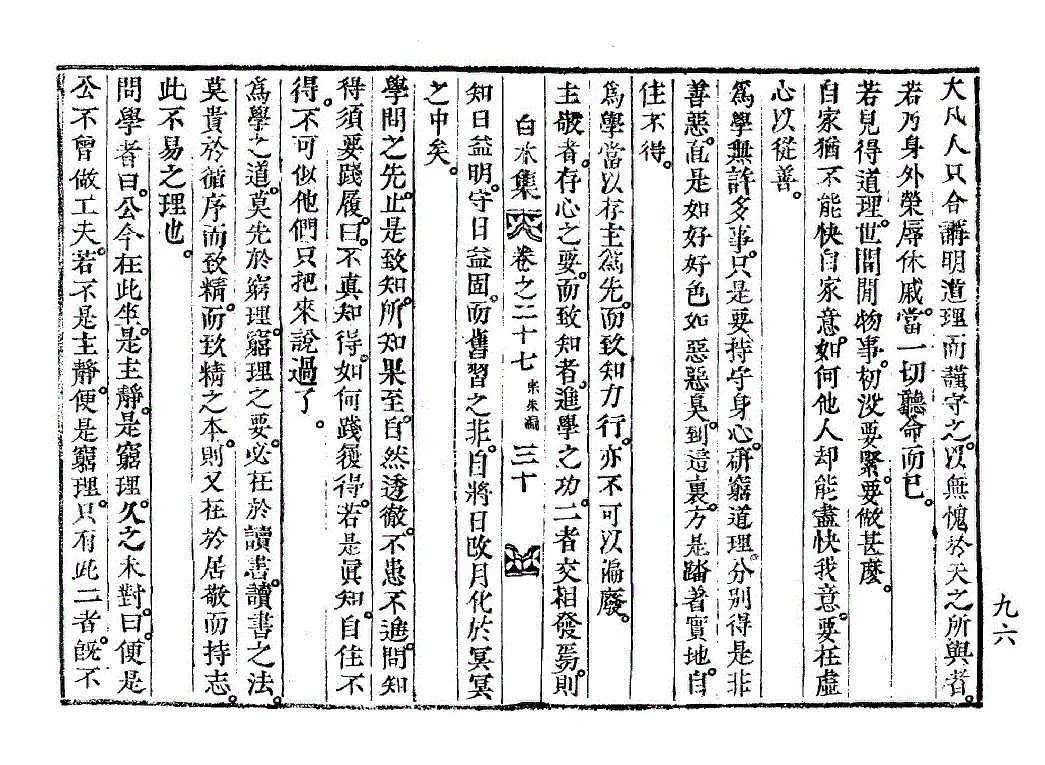 大凡人只合讲明道理而谨守之。以无愧于天之所与者。若乃身外荣辱休戚。当一切听命而已。
大凡人只合讲明道理而谨守之。以无愧于天之所与者。若乃身外荣辱休戚。当一切听命而已。若见得道理。世间閒物事。初没要紧。要做甚么。
自家犹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尽快我意。要在虚心以从善。
为学无许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穷道理。分别得是非善恶。直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到这里。方是踏着实地。自住不得。
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废。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旧习之非。自将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
学问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彻。不患不进。问知得须要践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践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们只把来说过了。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问学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静。是穷理。久之未对。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静。便是穷理。只有此二者。既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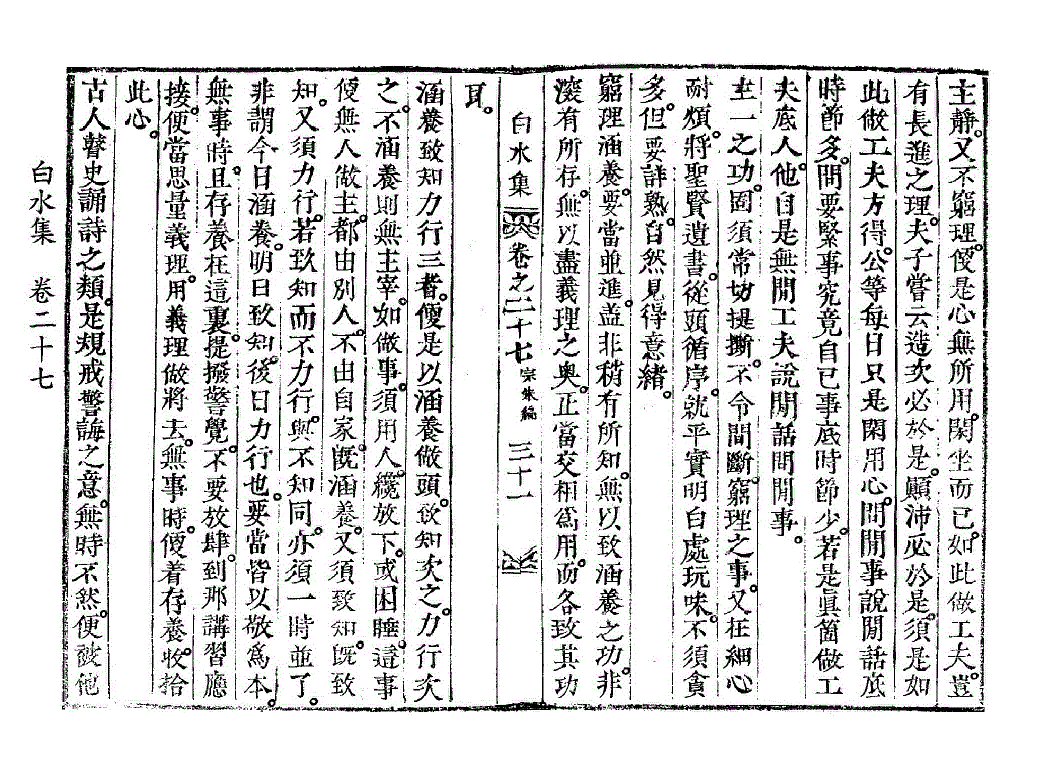 主静。又不穷理。便是心无所用。闲坐而已。如此做工夫。岂有长进之理。夫子尝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须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闲用心。问閒事说閒话底时节多。问要紧事究竟自己事底时节少。若是真个做工夫底人。他自是无閒工夫说閒话问閒事。
主静。又不穷理。便是心无所用。闲坐而已。如此做工夫。岂有长进之理。夫子尝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须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闲用心。问閒事说閒话底时节多。问要紧事究竟自己事底时节少。若是真个做工夫底人。他自是无閒工夫说閒话问閒事。主一之功。固须常切提撕。不令间断。穷理之事。又在细心耐烦。将圣贤遗书。从头循序。就平实明白处玩味。不须贪多。但要详熟。自然见得意绪。
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耳。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做头。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养则无主宰。如做事。须用人。才放下。或困睡。这事便无人做主。都由别人。不由自家。既涵养。又须致知。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亦须一时并了。非谓今日涵养。明日致知。后日力行也。要当皆以敬为本。无事时。且存养在这里。提拨警觉。不要放肆。到那讲习应接。便当思量义理。用义理做将去。无事时。便着存养。收拾此心。
古人瞽史诵诗之类。是规戒警诲之意。无时不然。便被他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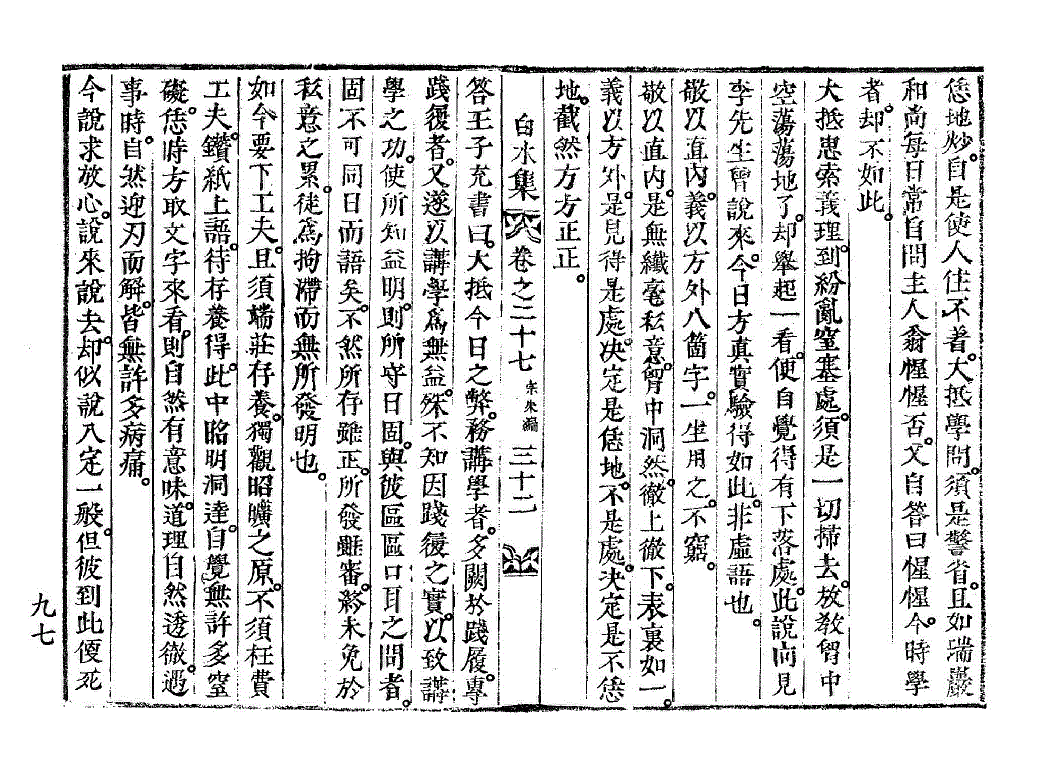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学问。须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常自问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时学者。却不如此。
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学问。须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常自问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时学者。却不如此。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此说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语也。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
敬以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义以方外。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是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
答王子充书曰。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专践履者。又遂以讲学为无益。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固。与彼区区口耳之问者。固不可同日而语矣。不然所存虽正。所发虽审。终未免于私意之累。徒为拘滞而无所发明也。
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中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恁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时。自然迎刃而解。皆无许多病痛。
今说求放心。说来说去。却似说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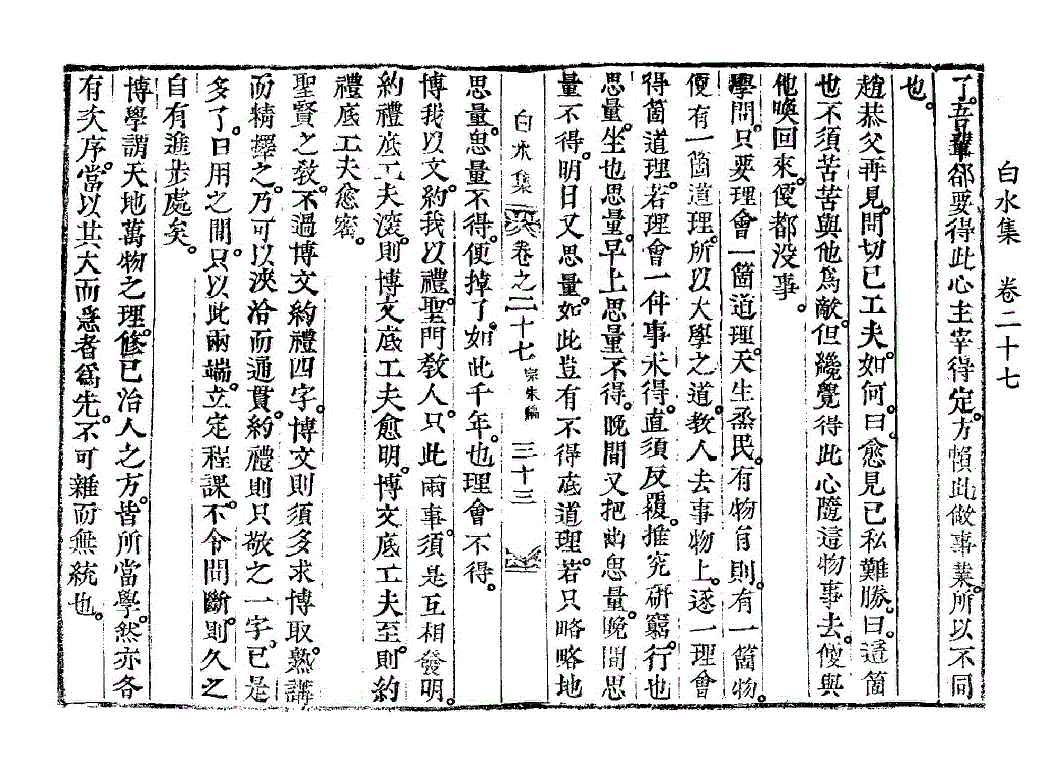 了。吾辈郤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也。
了。吾辈郤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所以不同也。赵恭父再见。问切己工夫。如何。曰。愈见己私难胜。曰。这个也不须苦苦与他为敌。但才觉得此心随这物事去。便与他唤回来。便都没事。
学问。只要理会一个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有一个物。便有一个道理。所以大学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会得个道理。若理会一件事未得。直须反覆。推究研穷。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间又把出思量。晚间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岂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会不得。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底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
圣贤之教。不过博文约礼四字。博文则须多求博取。熟讲而精择之。乃可以浃洽而通贯。约礼则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间。只以此两端。立定程课。不令问断。则久之自有进步处矣。
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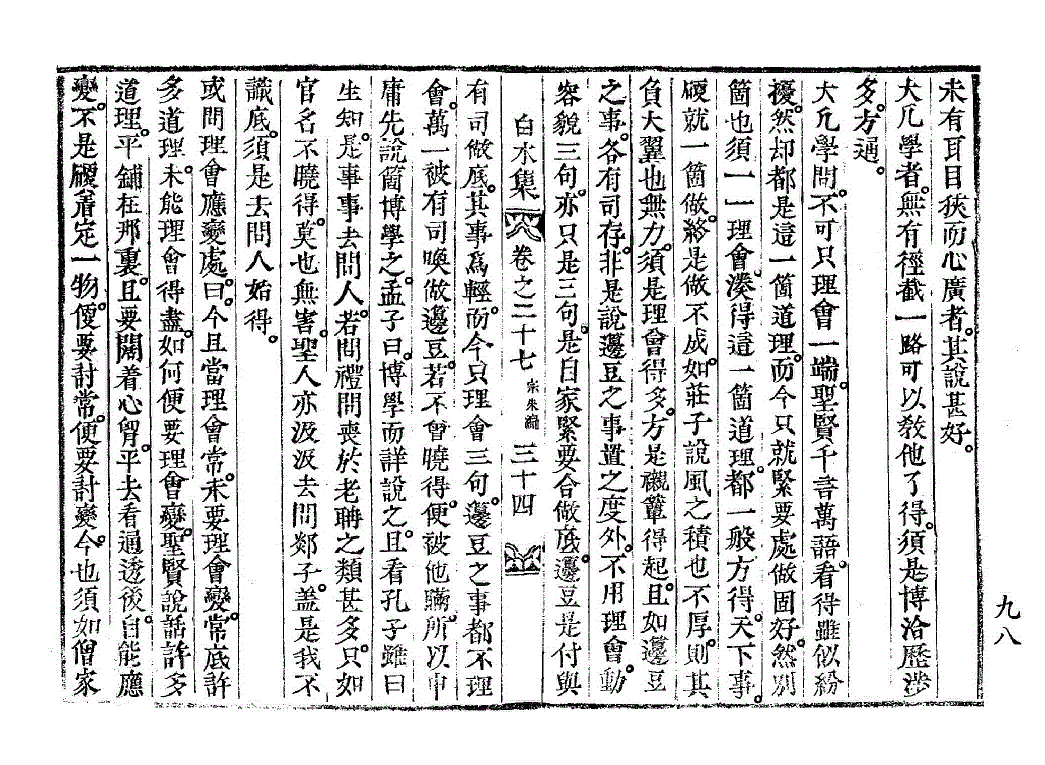 未有耳目狭而心广者。其说甚好。
未有耳目狭而心广者。其说甚好。大凡学者。无有径截一路可以教他了得。须是博洽历涉多。方通。
大凡学问。不可只理会一端。圣贤千言万语。看得虽似纷扰。然却都是这一个道理。而今只就紧要处做固好。然别个也须一一理会。凑得这一个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个做。终是做不成。如庄子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须是理会得多。方是衬簟得起。且如笾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说笾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会。动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紧要合做底。笾豆是付与有司做底。其事为轻。而今只理会三句。笾豆之事都不理会。万一被有司唤做笾豆。若不曾晓得。便被他瞒。所以中庸先说个博学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且看孔子虽曰生知。是事事去问人。若问礼问丧于老聃之类甚多。只如官名不晓得。莫也无害。圣人亦汲汲去问郯子。盖是我不识底。须是去问人始得。
或问理会应变处。曰。今且当理会常。未要理会变。常底许多道理。未能理会得尽。如何便要理会变。圣贤说话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且要阔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后。自能应变。不是硬着定一物。便要讨常。便要讨变。今也须如僧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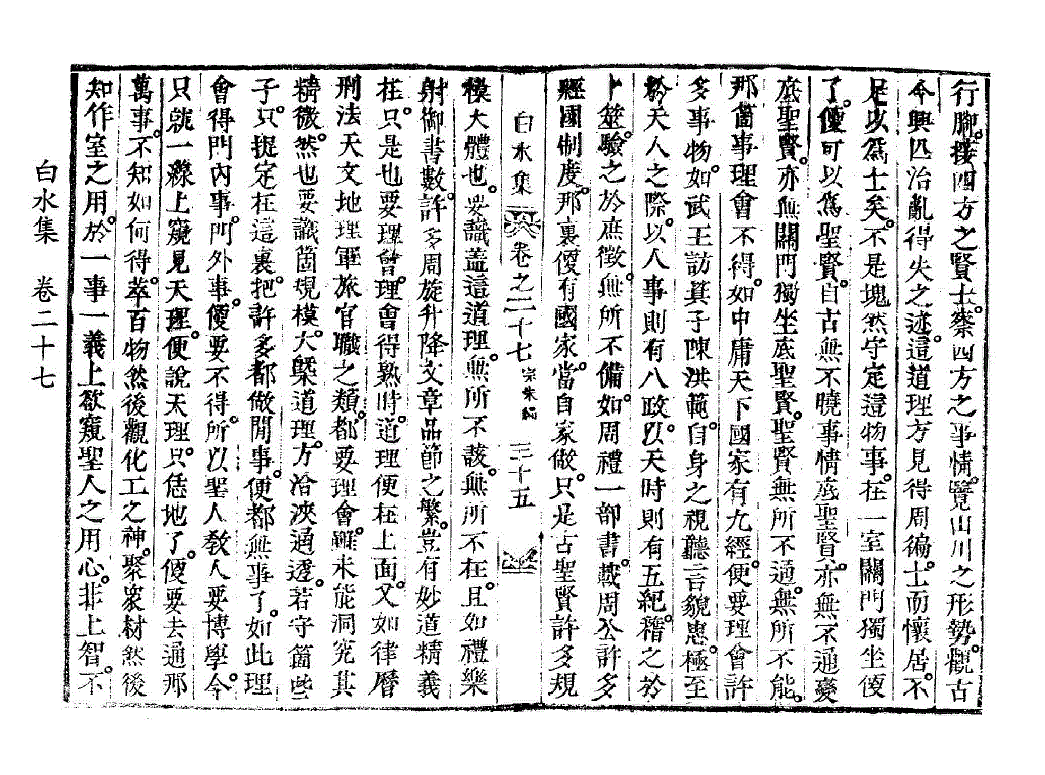 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事物。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徵。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槩道理。方洽浃通透。若守个些子。只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閒事。便都无事了。如此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要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今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
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事物。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徵。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槩道理。方洽浃通透。若守个些子。只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閒事。便都无事了。如此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要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今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9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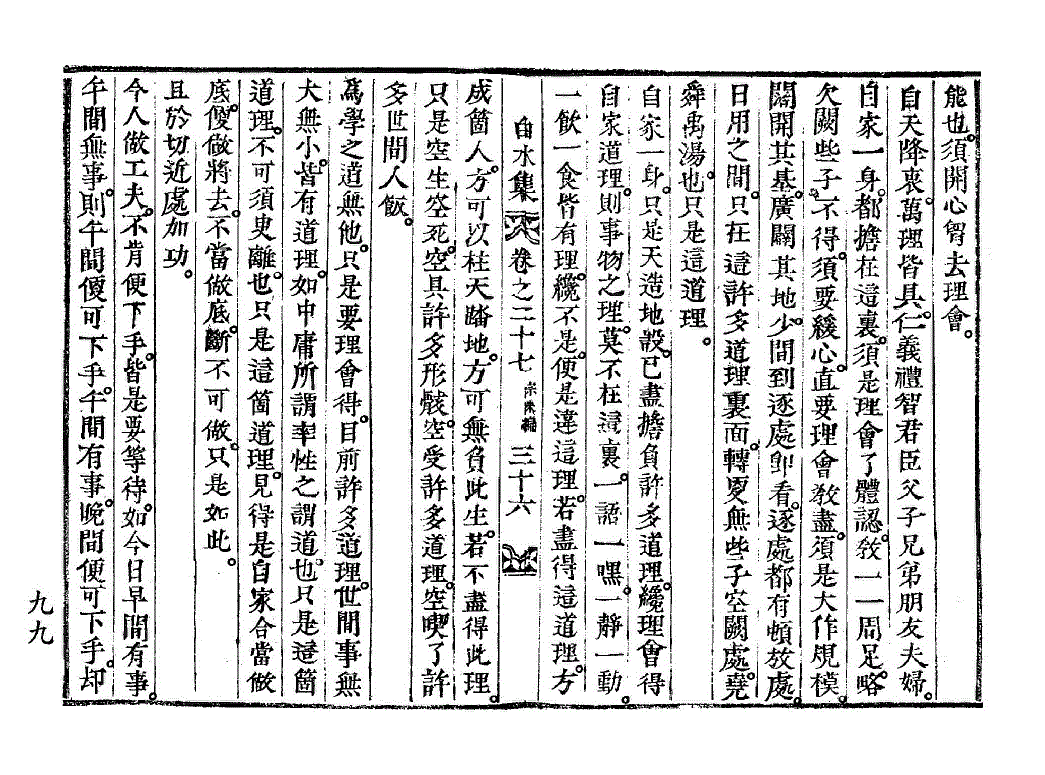 能也。须开心胸去理会。
能也。须开心胸去理会。自天降衷。万理皆具。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自家一身。都担在这里。须是理会了体认。教一一周足。略欠阙些子不得。须要缓心。直要理会教尽。须是大作规模。阔开其基。广辟其地。少间到逐处即看。逐处都有顿放处。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更无些子空阙处。尧舜禹汤。也只是这道理。
自家一身。只是天造地设。已尽担负许多道理。才理会得自家道理。则事物之理。莫不在这里。一语一嘿。一静一动。一饮一食皆有理。才不是。便是违这理。若尽得这道理。方成个人。方可以柱天踏地。方可无负此生。若不尽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许多形骸。空受许多道理。空吃了许多世间人饭。
为学之道无他。只是要理会得。目前许多道理。世间事无大无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也只是这个道理。不可须臾离。也只是这个道理。见得是自家合当做底。便做将去。不当做底。断不可做。只是如此。
且于切近处加功。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间有事。午间无事。则午间便可下手。午间有事。晚间便可下手。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10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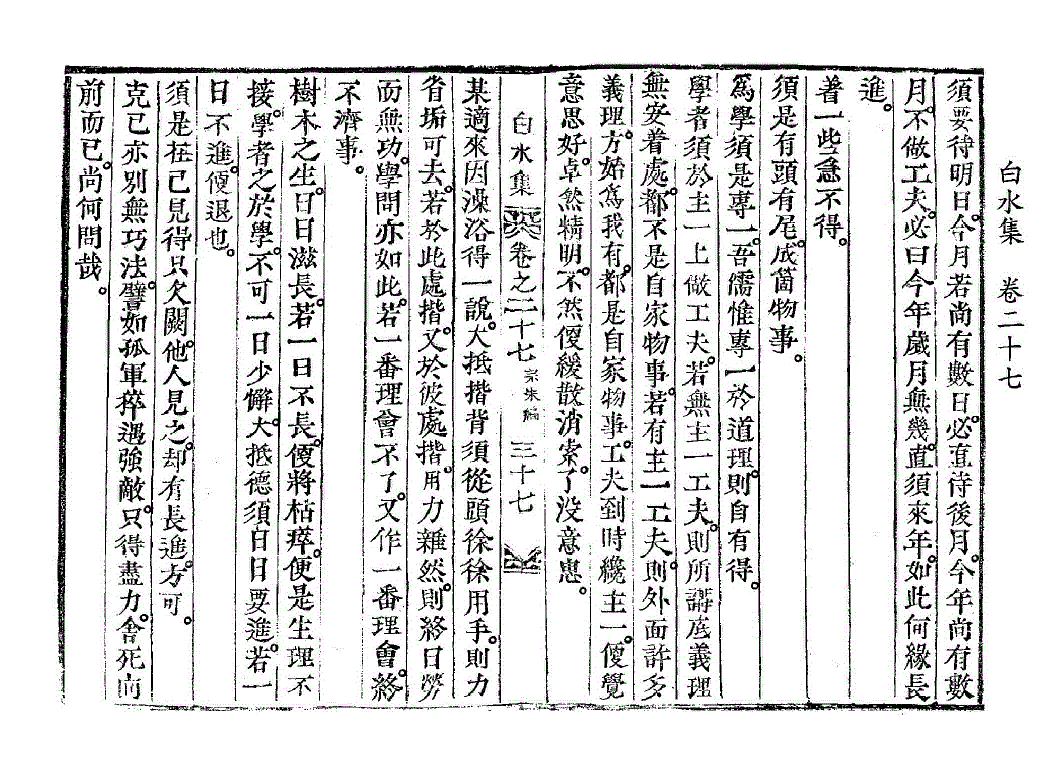 须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数日。必直待后月。今年尚有数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岁月无几。直须来年。如此何缘长进。
须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数日。必直待后月。今年尚有数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岁月无几。直须来年。如此何缘长进。着一些急不得。
须是有头有尾。成个物事。
为学须是专一。吾儒惟专一于道理。则自有得。
学者须于主一上做工夫。若无主一工夫。则所讲底义理无安着处。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则外面许多义理。方始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时才主一。便觉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缓散消索。了没意思。
某适来因澡浴得一说。大抵揩背须从头徐徐用手。则力省垢可去。若于此处揩。又于彼处揩。用力杂然。则终日劳而无功。学问亦如此。若一番理会不了。又作一番理会。终不济事。
树木之生。日日滋长。若一日不长。便将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学者之于学。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须日日要进。若一日不进。便退也。
须是在己见得只欠阙。他人见之。却有长进。方可。
克己亦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得尽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问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10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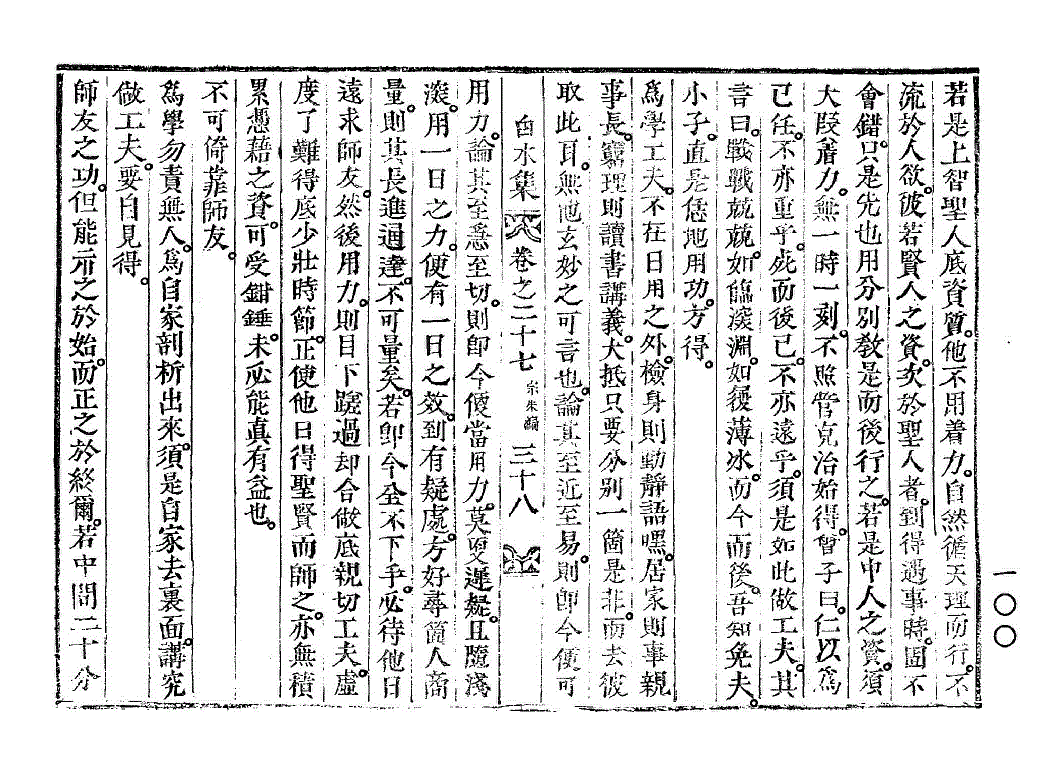 若是上智圣人底资质。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于人欲。彼若贤人之资。次于圣人者。到得遇事时。固不会错。只是先也用分别教是而后行之。若是中人之资。须大段着力。无一时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须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若是上智圣人底资质。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于人欲。彼若贤人之资。次于圣人者。到得遇事时。固不会错。只是先也用分别教是而后行之。若是中人之资。须大段着力。无一时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须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为学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检身则动静语嘿。居家则事亲事长。穷理则读书讲义。大抵只要分别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耳。无他玄妙之可言也。论其至近至易。则即今便可用力。论其至急至切。则即今便当用力。莫更迟疑。且随浅深。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处。方好寻个人商量。则其长进通达。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远求师友。然后用力。则目下蹉过却合做底亲切工夫。虚度了难得底少壮时节。正使他日得圣贤而师之。亦无积累凭藉之资。可受钳锤。未必能真有益也。
不可倚靠师友。
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要自见得。
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若中间二十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10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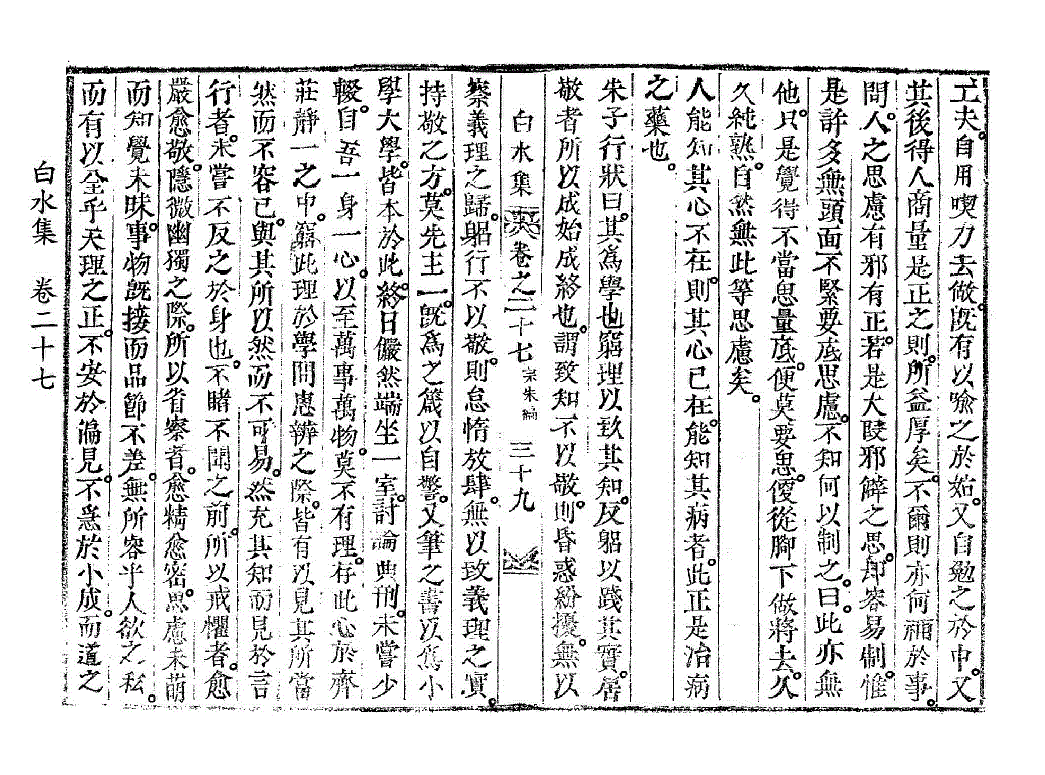 工夫。自用吃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之于中。又其后得人商量是正之则。所益厚矣。不尔则亦何补于事。
工夫。自用吃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之于中。又其后得人商量是正之则。所益厚矣。不尔则亦何补于事。问。人之思虑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许多无头面不紧要底思虑。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无他。只是觉得不当思量底。便莫要思。便从脚下做将去。久久纯熟。自然无此等思虑矣。
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能知其病者。此正是治病之药也。
朱子行状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刑。未尝少辍。自吾一身一心。以至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言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未昧。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10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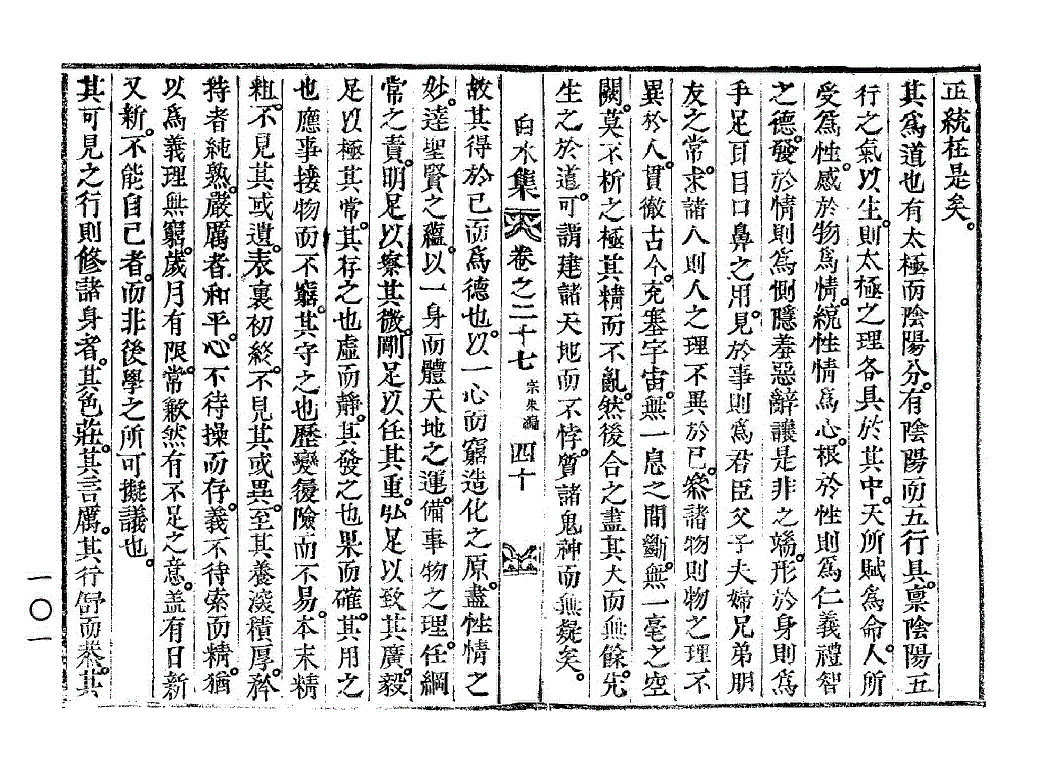 正统在是矣。
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馀。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矣。
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
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别集 第 10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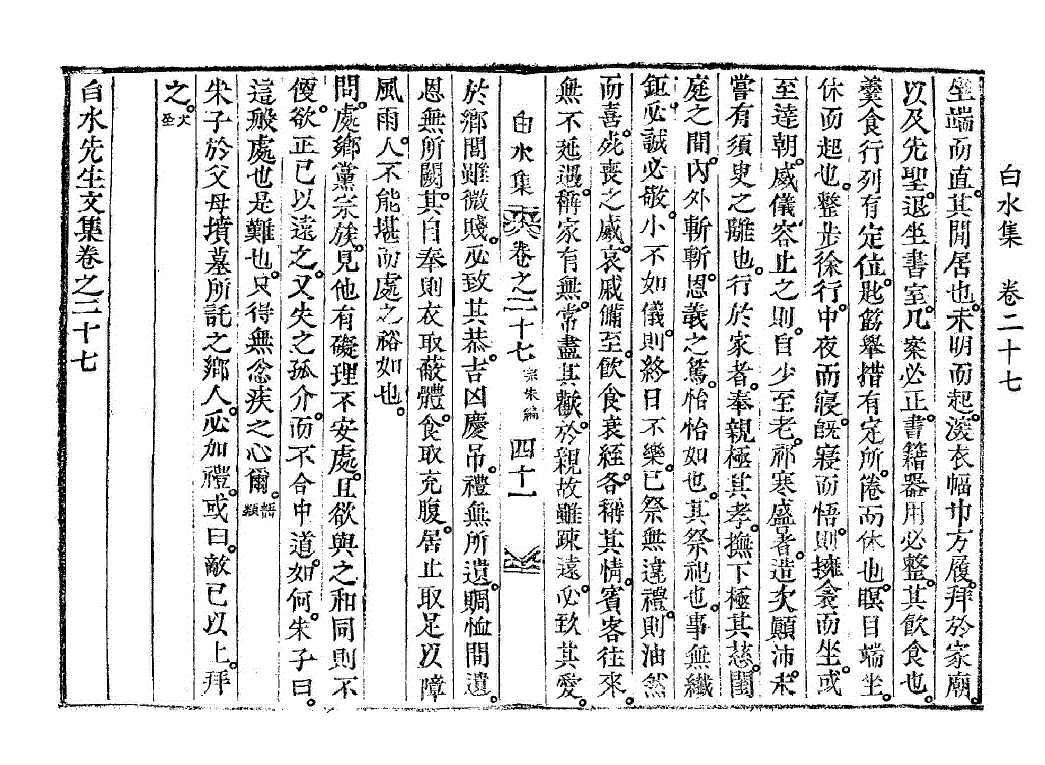 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悟。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朝。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威。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
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悟。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朝。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威。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问。处乡党宗族。见他有碍理不安处。且欲与之和同则不便。欲正己以远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朱子曰。这般处也是难也。只得无忿疾之心尔。(语类)
朱子于父母坟墓所托之乡人。必加礼。或曰。敌己以上。拜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