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论语讲说[上]
论语讲说[上]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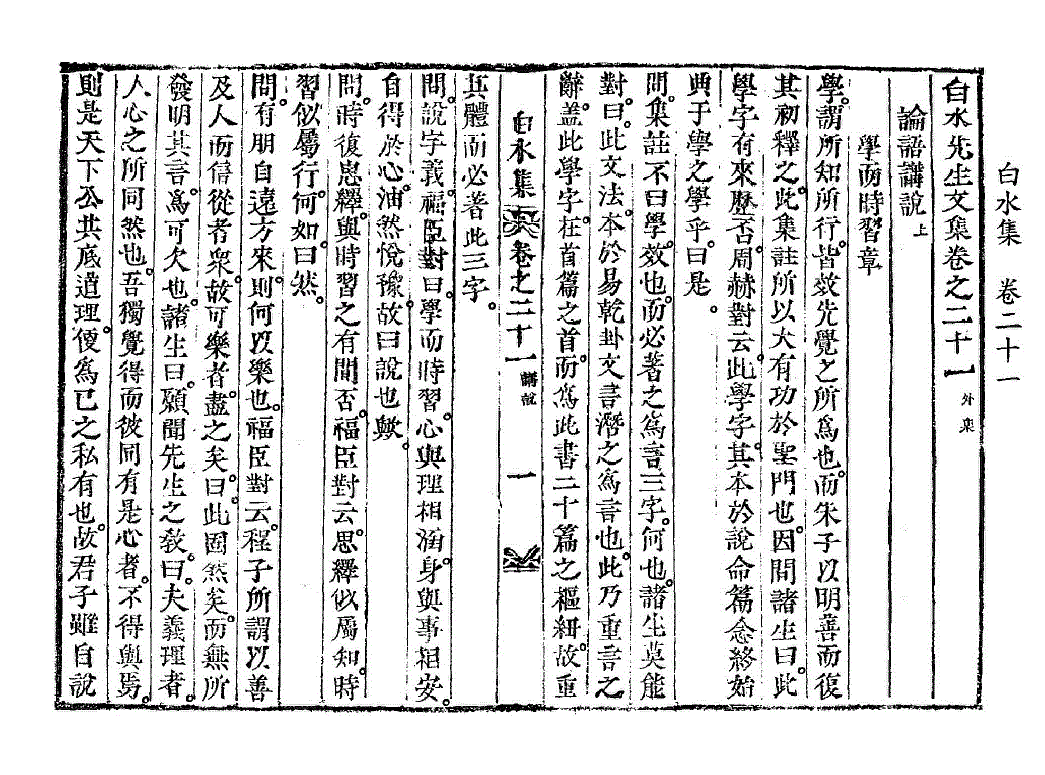 学而时习章
学而时习章学。谓所知所行。皆效先觉之所为也。而朱子以明善而复其初释之。此集注所以大有功于圣门也。因问诸生曰。此学字有来历否。周赫对云。此学字。其本于说命篇念终始典于学之学乎。曰是。
问。集注不曰学。效也。而必著之为言三字。何也。诸生莫能对。曰。此文法。本于易乾卦文言潜之为言也。此乃重言之辞。盖此学字。在首篇之首。而为此书二十篇之枢纽。故重其体而必著此三字。
问。说字义。福臣对曰。学而时习。心与理相涵。身与事相安。自得于心。油然悦豫。故曰说也欤。
问。时复思绎。与时习之有间否。福臣对云。思绎似属知。时习似属行。何如。曰然。
问。有朋自远方来。则何以乐也。福臣对云。程子所谓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者。尽之矣。曰。此固然矣。而无所发明其言。为可欠也。诸生曰。愿闻先生之教。曰。夫义理者。人心之所同然也。吾独觉得而彼同有是心者。不得与焉。则是天下公共底道理。便为己之私有也。故君子虽自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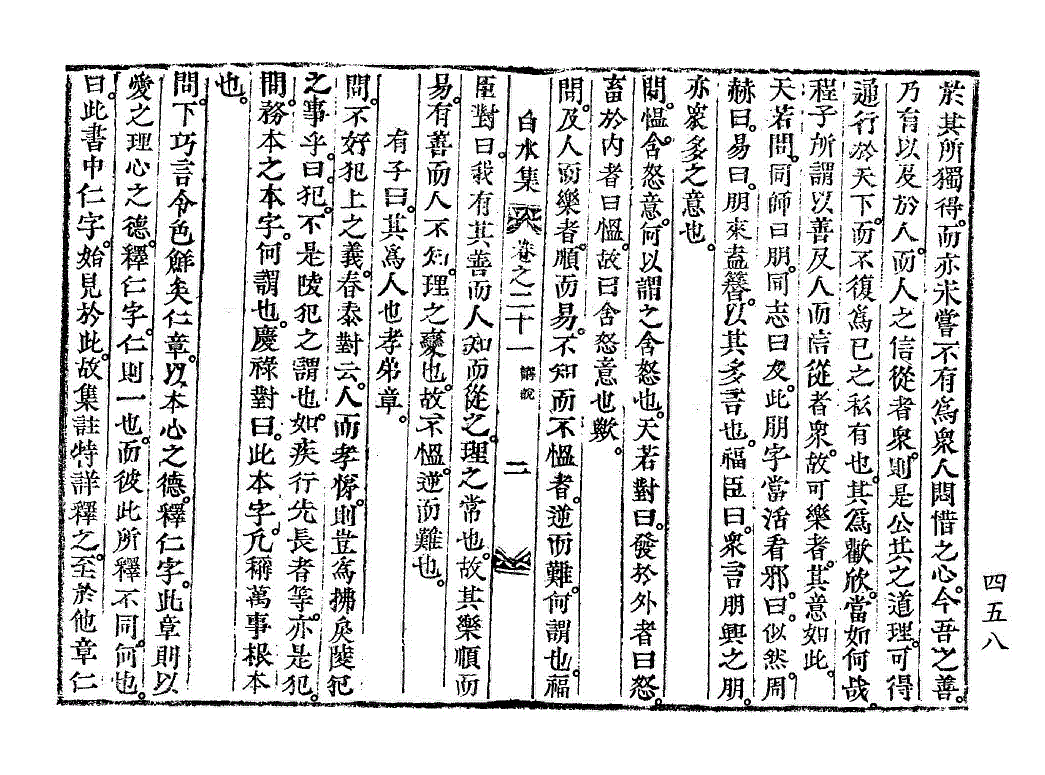 于其所独得。而亦未尝不有为众人闷惜之心。今吾之善。乃有以及于人。而人之信从者众。则是公共之道理。可得通行于天下。而不复为己之私有也。其为欢欣。当如何哉。程子所谓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者。其意如此。
于其所独得。而亦未尝不有为众人闷惜之心。今吾之善。乃有以及于人。而人之信从者众。则是公共之道理。可得通行于天下。而不复为己之私有也。其为欢欣。当如何哉。程子所谓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者。其意如此。天若问。同师曰朋。同志曰友。此朋字当活看邪。曰。似然。周赫曰。易曰。朋来盍簪。以其多言也。福臣曰。众言朋兴之朋。亦众多之意也。
问。愠。含怒意。何以谓之含怒也。天若对曰。发于外者曰怒。畜于内者曰愠。故曰含怒意也欤。
问。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何谓也。福臣对曰。我有其善而人知而从之。理之常也。故其乐顺而易。有善而人不知。理之变也。故不愠。逆而难也。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
问。不好犯上之义。春泰对云。人而孝悌。则岂为拂戾陵犯之事乎。曰。犯。不是陵犯之谓也。如疾行先长者等。亦是犯。
问。务本之本字。何谓也。庆禄对曰。此本字。凡称万事根本也。
问。下巧言令色鲜矣仁章。以本心之德。释仁字。此章则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字。仁则一也。而彼此所释不同。何也。曰。此书中仁字。始见于此。故集注特详释之。至于他章仁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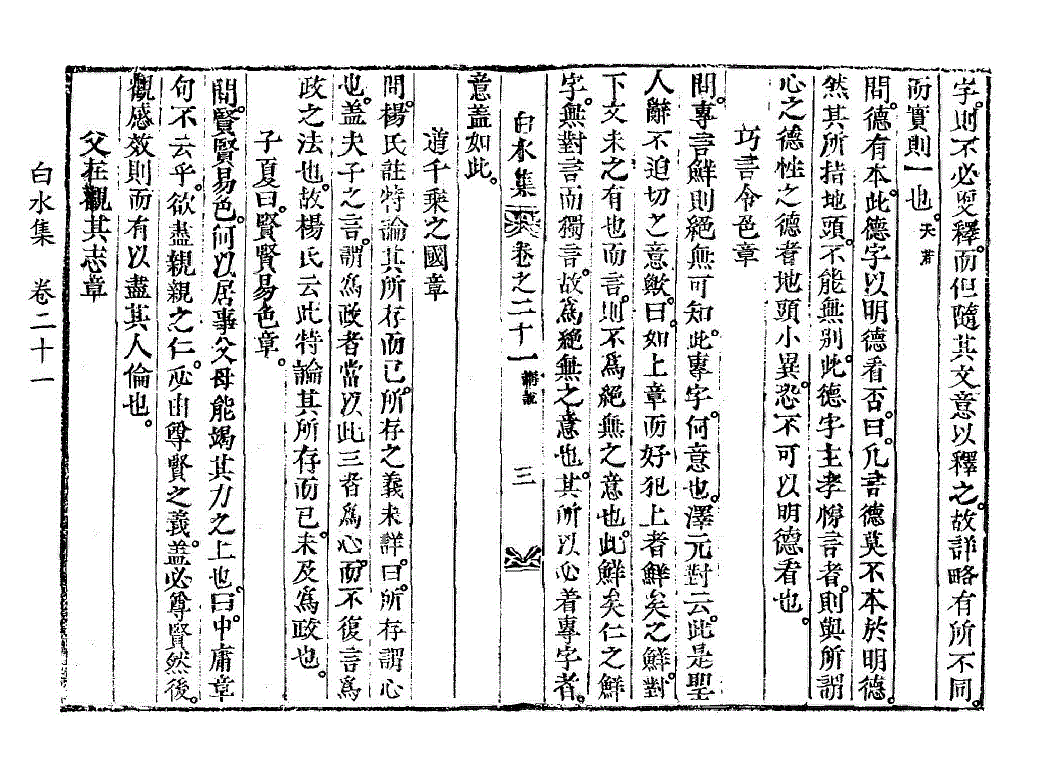 字。则不必更释。而但随其文意以释之。故详略有所不同。而实则一也。(天若)
字。则不必更释。而但随其文意以释之。故详略有所不同。而实则一也。(天若)问。德有本。此德字以明德看否。曰。凡言德莫不本于明德。然其所指地头。不能无别。此德字主孝悌言者。则与所谓心之德性之德者地头小异。恐不可以明德看也。
巧言令色章
问。专言鲜则绝无可知。此专字。何意也。泽元对云。此是圣人辞不迫切之意欤。曰。如上章而好犯上者鲜矣之鲜。对下文未之有也而言。则不为绝无之意也。此鲜矣仁之鲜字。无对言而独言。故为绝无之意也。其所以必着专字者。意盖如此。
道千乘之国章
问。杨氏注特论其所存而已。所存之义未详。曰。所存谓心也。盖夫子之言。谓为政者当以此三者为心。而不复言为政之法也。故杨氏云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
子夏曰。贤贤易色章。
问。贤贤易色。何以居事父母能竭其力之上也。曰。中庸章句不云乎。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盖必尊贤然后。观感效则而有以尽其人伦也。
父在观其志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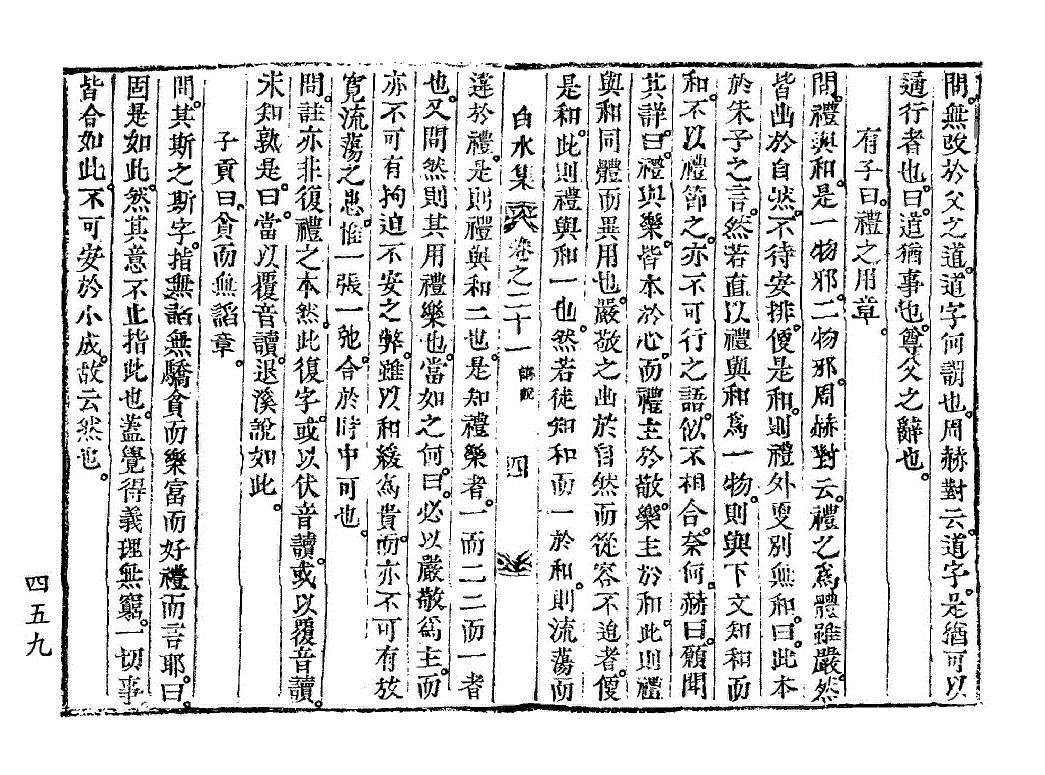 问。无改于父之道。道字何谓也。周赫对云。道字。是犹可以通行者也。曰。道犹事也。尊父之辞也。
问。无改于父之道。道字何谓也。周赫对云。道字。是犹可以通行者也。曰。道犹事也。尊父之辞也。有子曰。礼之用章。
问。礼与和。是一物邪。二物邪。周赫对云。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不待安排。便是和。则礼外更别无和。曰。此本于朱子之言。然若直以礼与和为一物。则与下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之语。似不相合。奈何。赫曰。愿闻其详。曰。礼与乐。皆本于心。而礼主于敬。乐主于和。此则礼与和同体而异用也。严敬之出于自然而从容不迫者。便是和。此则礼与和一也。然若徒知和而一于和。则流荡而违于礼。是则礼与和二也。是知礼乐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问然则其用礼乐也。当如之何。曰。必以严敬为主。而亦不可有拘迫不安之弊。虽以和缓为贵。而亦不可有放宽流荡之患。惟一张一弛。合于时中可也。
问。注亦非复礼之本然。此复字。或以伏音读。或以覆音读。未知孰是。曰。当以覆音读。退溪说如此。
子贡曰。贫而无谄章。
问。其斯之斯字。指无谄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而言耶。曰。固是如此。然其意不止指此也。盖觉得义理无穷。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于小成。故云然也。
为政以德章
问。为政以德。所可譬喻者。不止于北辰。而必以北辰为谕者。何也。曰。无为而天下归之之象。不以北辰为比而何。盖教人之道。莫若以象示之之为明晰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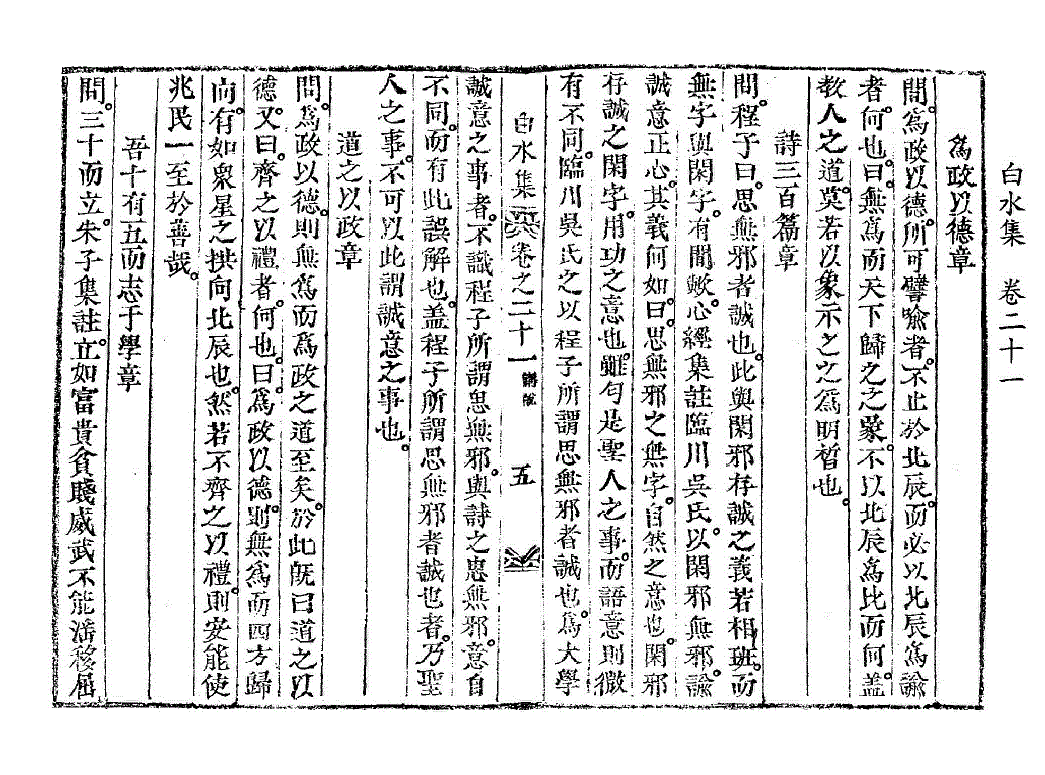 诗三百篇章
诗三百篇章问。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此与闲邪存诚之义若相班。而无字与闲字。有间欤。心经集注临川吴氏。以闲邪无邪。谕诚意正心。其义何如。曰。思无邪之无字。自然之意也。闲邪存诚之闲字。用功之意也。虽匀是圣人之事。而语意则微有不同。临川吴氏之以程子所谓思无邪者诚也。为大学诚意之事者。不识程子所谓思无邪。与诗之思无邪。意自不同。而有此误解也。盖程子所谓思无邪者诚也者。乃圣人之事。不可以此谓诚意之事也。
道之以政章
问。为政以德。则无为而为政之道至矣。于此既曰道之以德。又曰。齐之以礼者。何也。曰。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四方归向。有如众星之拱向北辰也。然若不齐之以礼。则安能使兆民一至于善哉。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
问。三十而立。朱子集注。立如富贵贫贱威武不能淫移屈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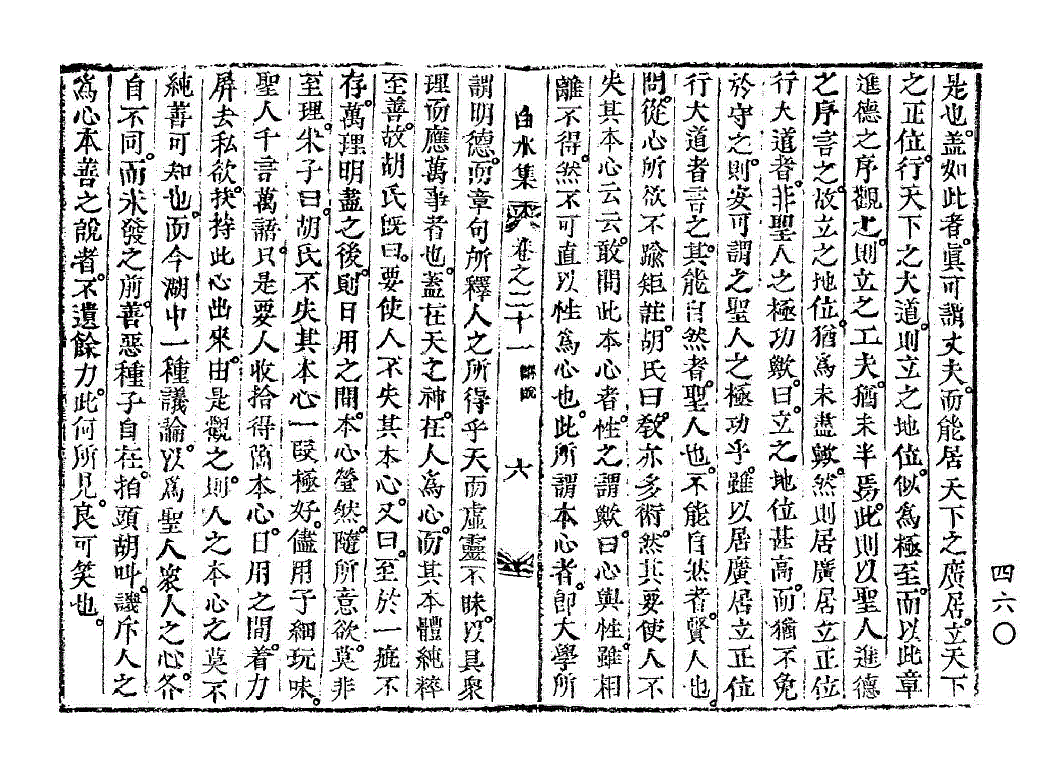 是也。盖如此者。真可谓丈夫。而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则立之地位。似为极至。而以此章进德之序观之。则立之工夫。犹未半焉。此则以圣人进德之序言之。故立之地位。犹为未尽欤。然则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者。非圣人之极功欤。曰。立之地位甚高。而犹不免于守之。则安可谓之圣人之极功乎。虽以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者言之。其能自然者。圣人也。不能自然者。贤人也。
是也。盖如此者。真可谓丈夫。而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则立之地位。似为极至。而以此章进德之序观之。则立之工夫。犹未半焉。此则以圣人进德之序言之。故立之地位。犹为未尽欤。然则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者。非圣人之极功欤。曰。立之地位甚高。而犹不免于守之。则安可谓之圣人之极功乎。虽以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者言之。其能自然者。圣人也。不能自然者。贤人也。问。从心所欲不踰矩注。胡氏曰。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云云。敢问此本心者。性之谓欤。曰心与性。虽相离不得。然不可直以性为心也。此所谓本心者。即大学所谓明德。而章句所释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盖在天之神。在人为心。而其本体纯粹至善。故胡氏既曰。要使人不失其本心。又曰。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极好。尽用子细玩味。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日用之间。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来。由是观之。则人之本心之莫不纯善可知也。而今湖中一种议论。以为圣人众人之心。各自不同。而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拍头胡叫。讥斥人之为心本善之说者。不遗馀力。此何所见。良可笑也。
温故而知新章
问。知行并进然后。可以为人师。温故而知新。似是专指知而言也。朱子故以每有新得补本意。得者非兼言行道而有得之得也欤。曰。知行兼尽然后。可以为人师。然此章则专以知言也。朱子每有新得之训。初非补经之言也。然知而不行。则不能真知。必也躬行心得然后。乃为真知。故书无逸。以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君为迪哲。以是推之。则时习二字中。亦自有行意。而若以新得之得字。谓兼行意则不可。行道而有得于心之得字。亦是知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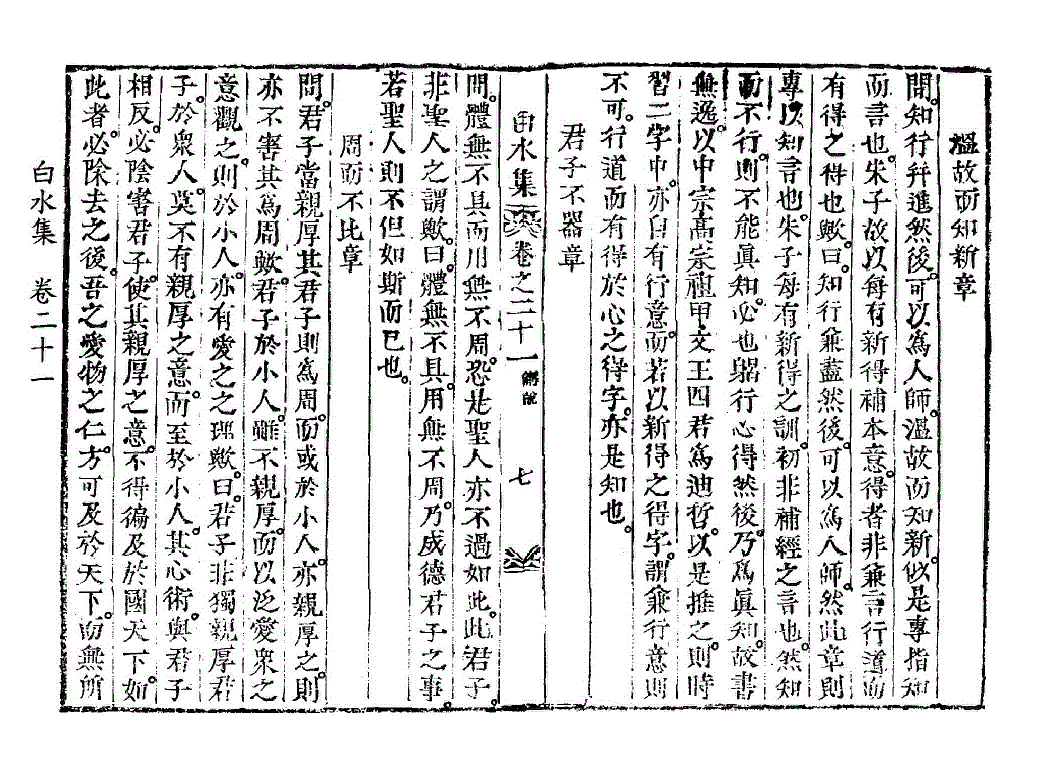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章问。体无不具而用无不周。恐是圣人亦不过如此。此君子。非圣人之谓欤。曰。体无不具。用无不周。乃成德君子之事。若圣人则不但如斯而已也。
周而不比章
问。君子当亲厚其君子则为周。而或于小人。亦亲厚之。则亦不害其为周欤。君子于小人。虽不亲厚。而以泛爱众之意观之。则于小人。亦有爱之之理欤。曰。君子非独亲厚君子。于众人。莫不有亲厚之意。而至于小人。其心术。与君子相反。必阴害君子。使其亲厚之意。不得遍及于国天下。如此者。必除去之后。吾之爱物之仁。方可及于天下。而无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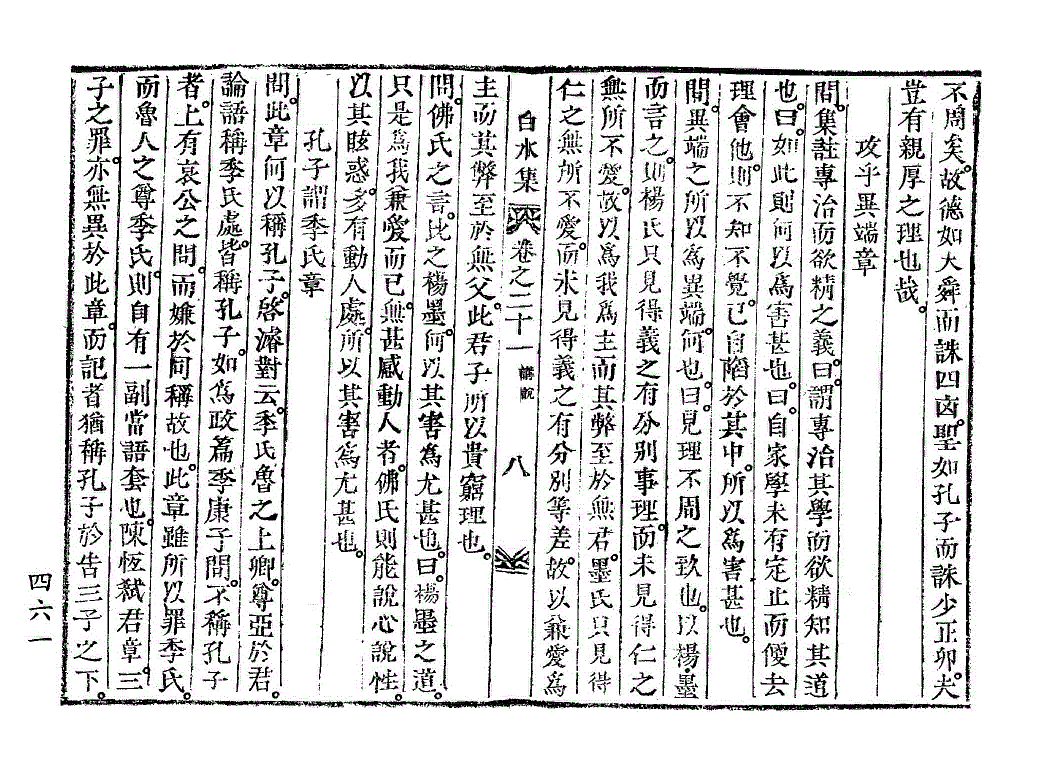 不周矣。故德如大舜而诛四凶。圣如孔子而诛少正卯。夫岂有亲厚之理也哉。
不周矣。故德如大舜而诛四凶。圣如孔子而诛少正卯。夫岂有亲厚之理也哉。攻乎异端章
问。集注专治而欲精之义。曰。谓专治其学而欲精知其道也。曰。如此则何以为害甚也。曰。自家学未有定止而便去理会他。则不知不觉。已自陷于其中。所以为害甚也。
问。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何也。曰。见理不周之致也。以杨,墨而言之。则杨氏只见得义之有分别事理。而未见得仁之无所不爱。故以为我为主而其弊至于无君。墨氏只见得仁之无所不爱。而未见得义之有分别等差。故以兼爱为主而其弊至于无父。此君子所以贵穷理也。
问。佛氏之言。比之杨墨。何以其害为尤甚也。曰。杨墨之道。只是为我兼爱而已。无甚感动人者。佛氏则能说心说性。以其眩惑。多有动人处。所以其害为尤甚也。
孔子谓季氏章
问。此章何以称孔子。启浚对云。季氏鲁之上卿。尊亚于君。论语称季氏处。皆称孔子。如为政篇季康子问。不称孔子者。上有哀公之问。而嫌于同称故也。此章虽所以罪季氏。而鲁人之尊季氏。则自有一副当语套也。陈恒弑君章。三子之罪。亦无异于此章。而记者犹称孔子于告三子之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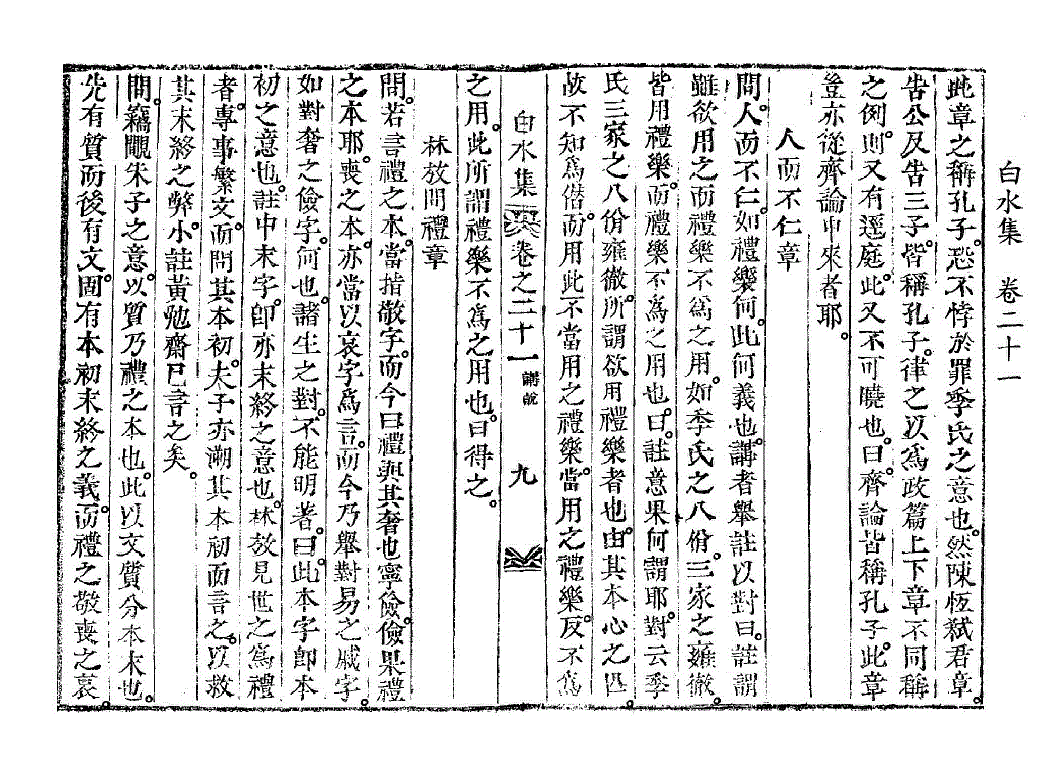 此章之称孔子。恐不悖于罪季氏之意也。然陈恒弑君章。告公及告三子。皆称孔子。律之以为政篇上下章不同称之例。则又有径庭。此又不可晓也。曰。齐论皆称孔子。此章岂亦从齐论中来者耶。
此章之称孔子。恐不悖于罪季氏之意也。然陈恒弑君章。告公及告三子。皆称孔子。律之以为政篇上下章不同称之例。则又有径庭。此又不可晓也。曰。齐论皆称孔子。此章岂亦从齐论中来者耶。人而不仁章
问。人而不仁。如礼乐何。此何义也。讲者举注以对曰。注谓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彻。皆用礼乐。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曰。注意果何谓耶。对云季氏三家之八佾雍彻。所谓欲用礼乐者也。由其本心之亡。故不知为僭。而用此不当用之礼乐。当用之礼乐。反不为之用。此所谓礼乐不为之用也。曰得之。
林放问礼章
问。若言礼之本。当指敬字。而今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俭果礼之本耶。丧之本。亦当以哀字为言。而今乃举对易之戚字。如对奢之俭字。何也。诸生之对。不能明著。曰。此本字即本初之意也。注中末字。即亦末终之意也。林放见世之为礼者。专事繁文。而问其本初。夫子亦溯其本初而言之。以救其末终之弊。小注黄勉斋已言之矣。
问。窃覸朱子之意。以质乃礼之本也。此以文质分本末也。先有质而后有文。固有本初末终之义。而礼之敬丧之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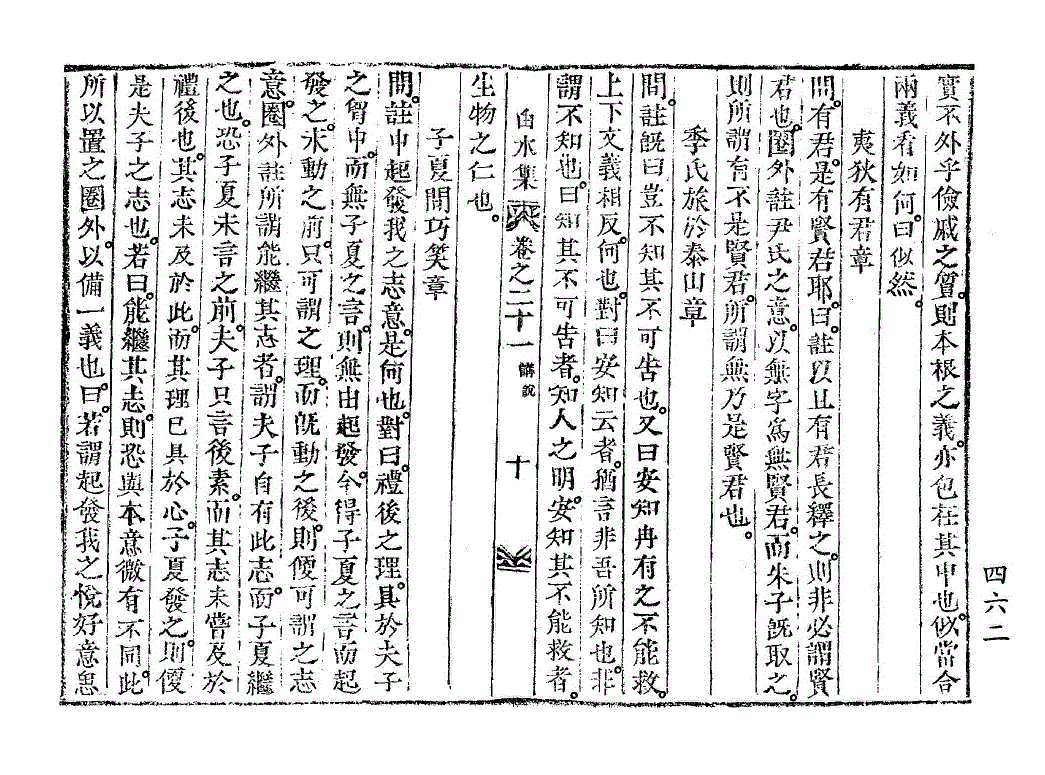 实不外乎俭戚之质。则本根之义。亦包在其中也。似当合两义看如何。曰似然。
实不外乎俭戚之质。则本根之义。亦包在其中也。似当合两义看如何。曰似然。夷狄有君章
问。有君。是有贤君耶。曰。注以且有君长释之。则非必谓贤君也。圈外注尹氏之意。以无字为无贤君。而朱子既取之。则所谓有不是贤君。所谓无乃是贤君也。
季氏旅于泰山章
问。注既曰岂不知其不可告也。又曰安知冉有之不能救。上下文义相反。何也。对曰安知云者。犹言非吾所知也。非谓不知也。曰知其不可告者。知人之明。安知其不能救者。生物之仁也。
子夏问巧笑章
问。注中起发我之志意。是何也。对曰。礼后之理。具于夫子之胸中。而无子夏之言。则无由起发。今得子夏之言而起发之。未动之前。只可谓之理。而既动之后。则便可谓之志意。圈外注所谓能继其志者。谓夫子自有此志。而子夏继之也。恐子夏未言之前。夫子只言后素。而其志未尝及于礼后也。其志未及于此。而其理已具于心。子夏发之。则便是夫子之志也。若曰。能继其志。则恐与本意微有不同。此所以置之圈外。以备一义也。曰。若谓起发我之悦好意思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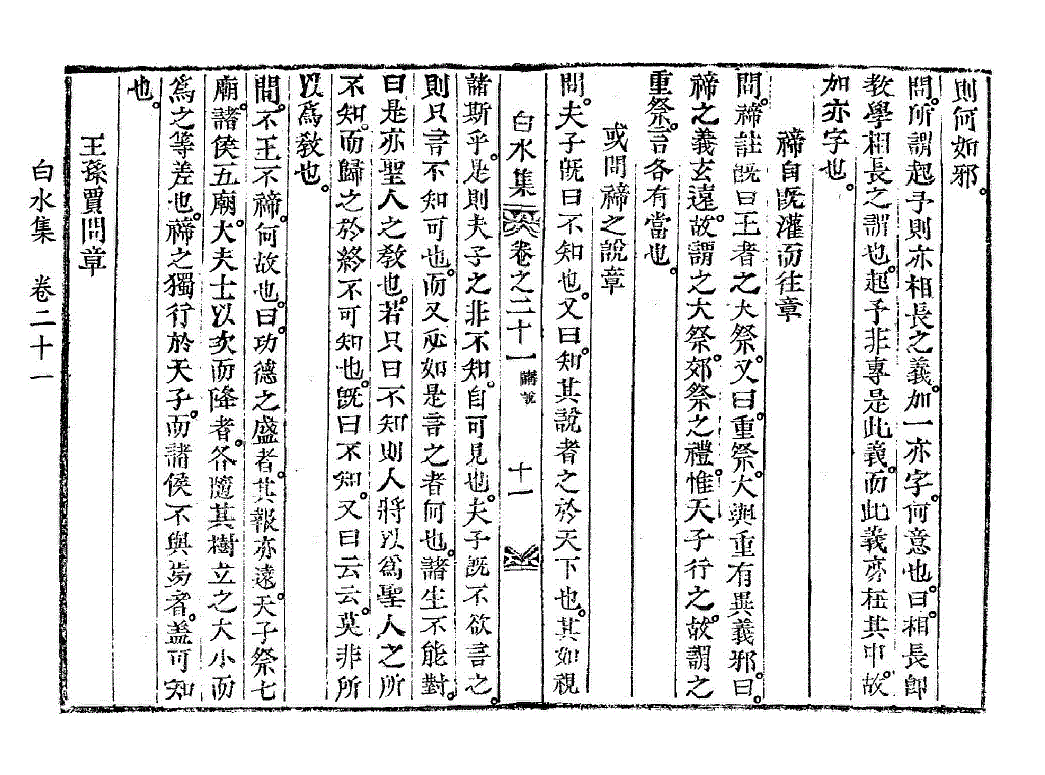 则何如邪。
则何如邪。问。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加一亦字。何意也。曰。相长即教学相长之谓也。起予非专是此义。而此义亦在其中。故加亦字也。
禘自既灌而往章
问。禘注既曰王者之大祭。又曰。重祭。大与重有异义邪。曰。禘之义玄远。故谓之大祭。郊祭之礼。惟天子行之。故谓之重祭。言各有当也。
或问禘之说章
问。夫子既曰不知也。又曰。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视诸斯乎。是则夫子之非不知。自可见也。夫子既不欲言之。则只言不知可也。而又必如是言之者何也。诸生不能对。曰是亦圣人之教也。若只曰不知则人将以为圣人之所不知。而归之于终不可知也。既曰不知。又曰云云。莫非所以为教也。
问。不王不禘。何故也。曰。功德之盛者。其报亦远。天子祭七庙。诸侯五庙。大夫士以次而降者。各随其树立之大小而为之等差也。禘之独行于天子。而诸侯不与焉者。盖可知也。
王孙贾问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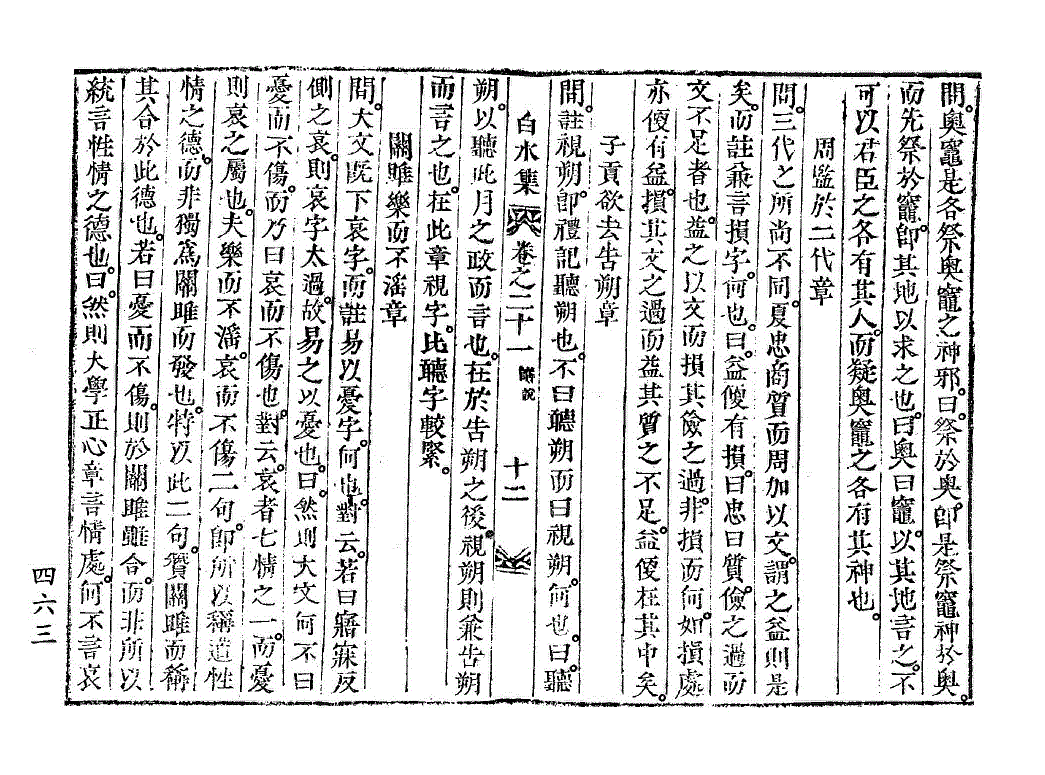 问。奥灶是各祭奥灶之神邪。曰。祭于奥。即是祭灶神于奥。而先祭于灶。即其地以求之也。曰奥曰灶。以其地言之。不可以君臣之各有其人。而疑奥灶之各有其神也。
问。奥灶是各祭奥灶之神邪。曰。祭于奥。即是祭灶神于奥。而先祭于灶。即其地以求之也。曰奥曰灶。以其地言之。不可以君臣之各有其人。而疑奥灶之各有其神也。周监于二代章
问。三代之所尚不同。夏忠商质而周加以文。谓之益则是矣。而注兼言损字。何也。曰。益便有损。曰忠曰质。俭之过而文不足者也。益之以文而损其俭之过。非损而何。如损处亦便有益。损其文之过而益其质之不足。益便在其中矣。
子贡欲去告朔章
问。注视朔。即礼记听朔也。不曰听朔而曰视朔。何也。曰。听朔。以听此月之政而言也。在于告朔之后。视朔则兼告朔而言之也。在此章视字。比听字较紧。
关雎乐而不淫章
问。大文既下哀字。而注易以忧字。何也。对云。若曰寤寐反侧之哀。则哀字太过。故易之以忧也。曰。然则大文何不曰忧而不伤。而乃曰哀而不伤也。对云。哀者七情之一。而忧则哀之属也。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句。即所以称道性情之德。而非独为关雎而发也。特以此二句。赞关雎而称其合于此德也。若曰忧而不伤。则于关雎虽合。而非所以统言性情之德也。曰。然则大学正心章言情处。何不言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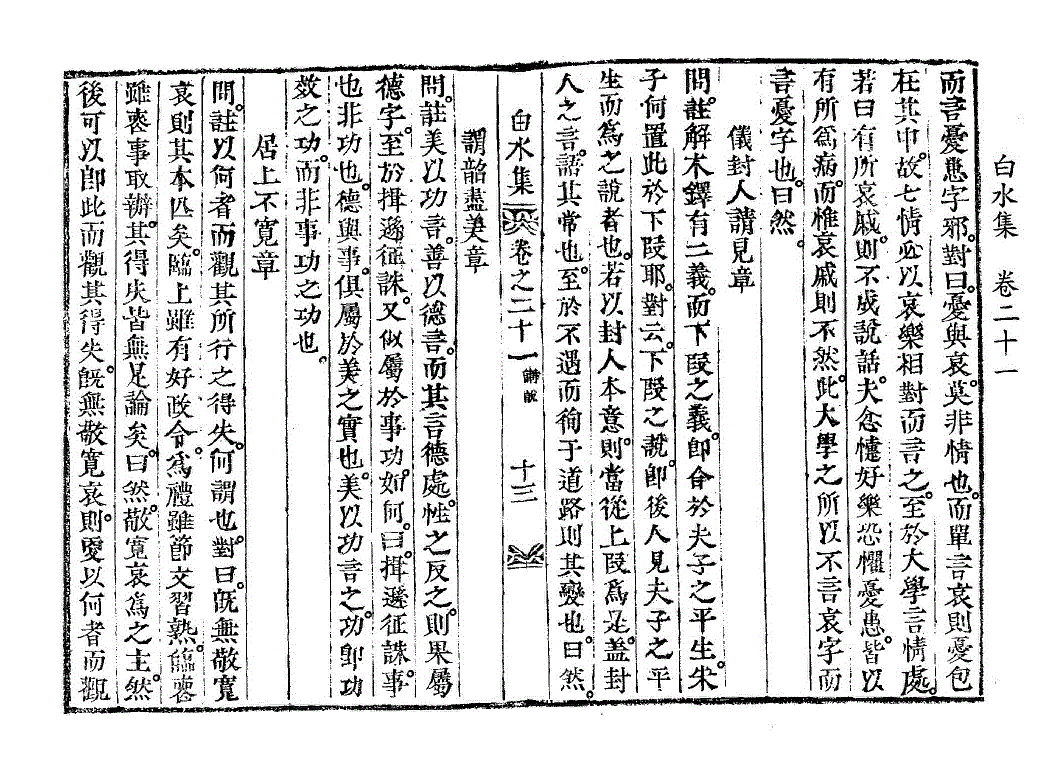 而言忧患字邪。对曰。忧与哀。莫非情也。而单言哀则忧包在其中。故七情必以哀乐相对而言之。至于大学言情处。若曰有所哀戚。则不成说话。夫忿懥好乐恐惧忧患。皆以有所为病。而惟哀戚则不然。此大学之所以不言哀字而言忧字也。曰然。
而言忧患字邪。对曰。忧与哀。莫非情也。而单言哀则忧包在其中。故七情必以哀乐相对而言之。至于大学言情处。若曰有所哀戚。则不成说话。夫忿懥好乐恐惧忧患。皆以有所为病。而惟哀戚则不然。此大学之所以不言哀字而言忧字也。曰然。仪封人请见章
问。注解木铎有二义。而下段之义。即合于夫子之平生。朱子何置此于下段耶。对云。下段之说。即后人见夫子之平生而为之说者也。若以封人本意。则当从上段为是。盖封人之言。语其常也。至于不遇而徇于道路则其变也。曰然。
谓韶尽美章
问。注美以功言。善以德言。而其言德处。性之反之。则果属德字。至于揖逊征诛。又似属于事功。如何。曰。揖逊征诛。事也非功也。德与事。俱属于美之实也。美以功言之。功即功效之功。而非事功之功也。
居上不宽章
问。注以何者而观其所行之得失。何谓也。对曰。既无敬宽哀则其本亡矣。临上虽有好政令。为礼虽节文习熟。临丧虽丧事取办。其得失皆无足论矣。曰然。敬宽哀为之主。然后可以即此而观其得失。既无敬宽哀。则更以何者而观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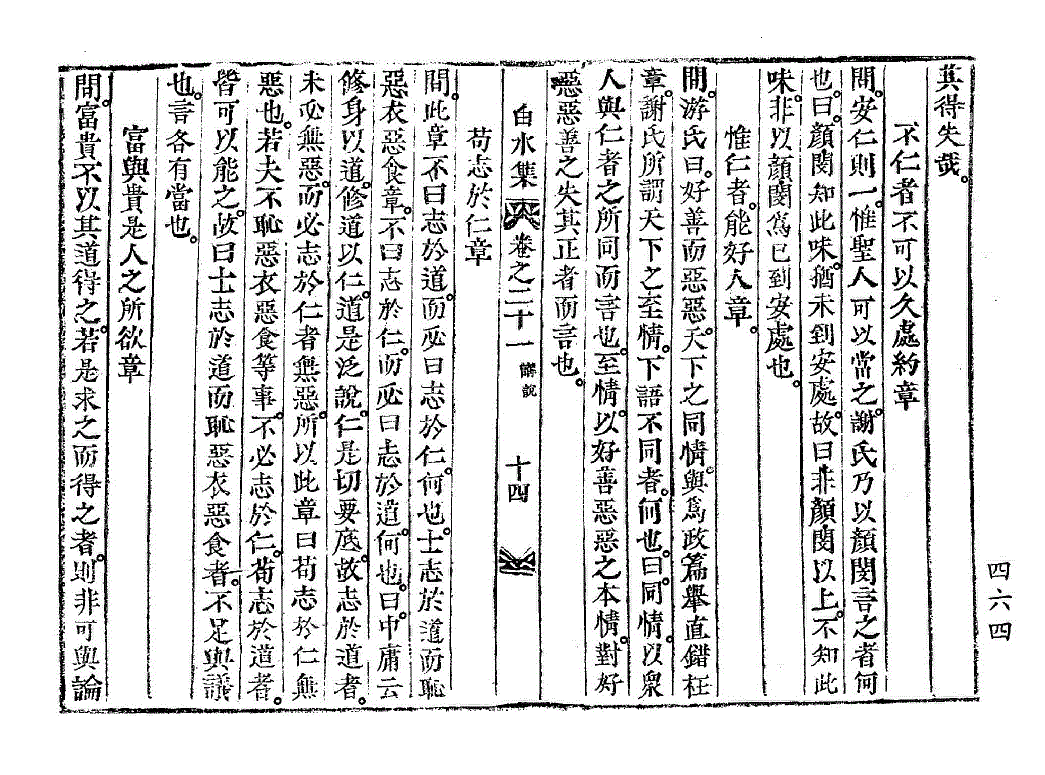 其得失哉。
其得失哉。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问。安仁则一。惟圣人可以当之。谢氏乃以颜闵言之者何也。曰。颜,闵知此味。犹未到安处。故曰非颜,闵以上。不知此味。非以颜,闵为已到安处也。
惟仁者。能好人章。
问。游氏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与为政篇举直错枉章。谢氏所谓天下之至情。下语不同者。何也。曰。同情。以众人与仁者之所同而言也。至情。以好善恶恶之本情。对好恶恶善之失其正者而言也。
苟志于仁章
问。此章不曰志于道。而必曰志于仁。何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章。不曰志于仁。而必曰志于道。何也。曰。中庸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是泛说。仁是切要底。故志于道者。未必无恶。而必志于仁者无恶。所以此章曰苟志于仁无恶也。若夫不耻恶衣恶食等事。不必志于仁。苟志于道者。皆可以能之。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言各有当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章
问。富贵不以其道得之。若是求之而得之者。则非可与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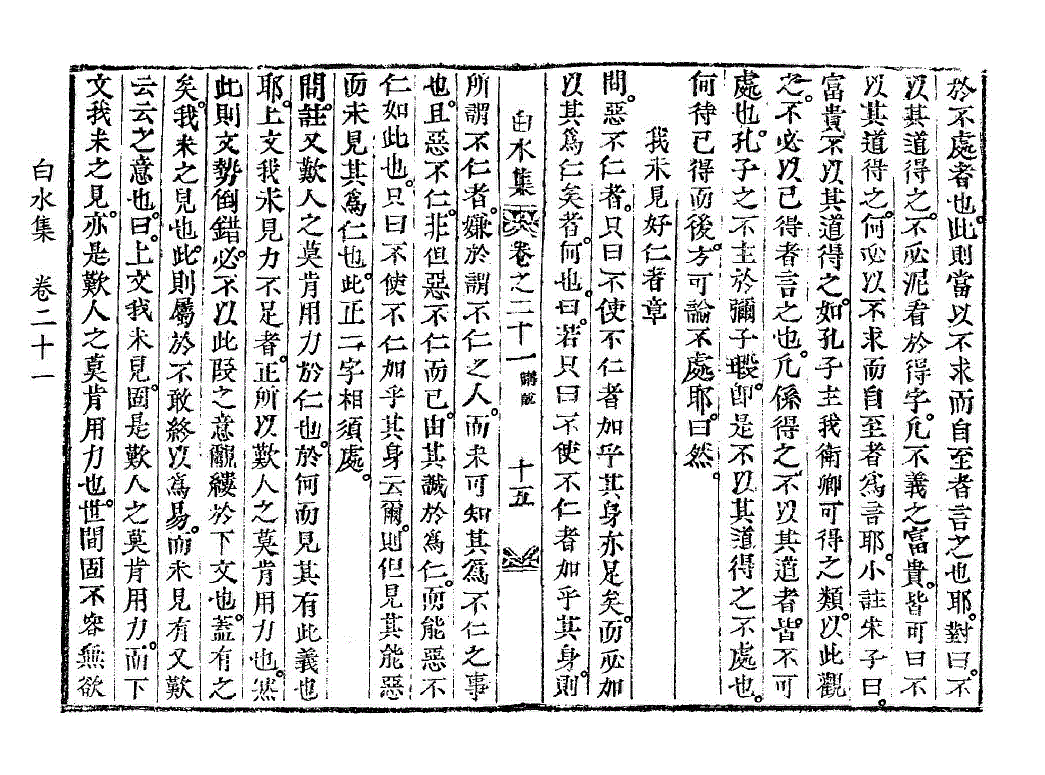 于不处者也。此则当以不求而自至者言之也耶。对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必泥看于得字。凡不义之富贵。皆可曰不以其道得之。何必以不求而自至者为言耶。小注朱子曰。富贵不以其道得之。如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之类。以此观之。不必以已得者言之也。凡系得之不以其道者。皆不可处也。孔子之不主于弥子瑕。即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何待已得而后。方可论不处耶。曰然。
于不处者也。此则当以不求而自至者言之也耶。对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必泥看于得字。凡不义之富贵。皆可曰不以其道得之。何必以不求而自至者为言耶。小注朱子曰。富贵不以其道得之。如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之类。以此观之。不必以已得者言之也。凡系得之不以其道者。皆不可处也。孔子之不主于弥子瑕。即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何待已得而后。方可论不处耶。曰然。我未见好仁者章
问。恶不仁者。只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亦足矣。而必加以其为仁矣者。何也。曰。若只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则所谓不仁者。嫌于谓不仁之人。而未可知其为不仁之事也。且恶不仁。非但恶不仁而已。由其诚于为仁。而能恶不仁如此也。只曰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云尔。则但见其能恶而未见其为仁也。此正二字相须处。
问。注又叹人之莫肯用力于仁也。于何而见其有此义也耶。上文我未见力不足者。正所以叹人之莫肯用力也。然此则文势倒错。必不以此段之意覼缕于下文也。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此则属于不敢终以为易。而未见有又叹云云之意也。曰。上文我未见。固是叹人之莫肯用力。而下文我未之见。亦是叹人之莫肯用力也。世间固不容无欲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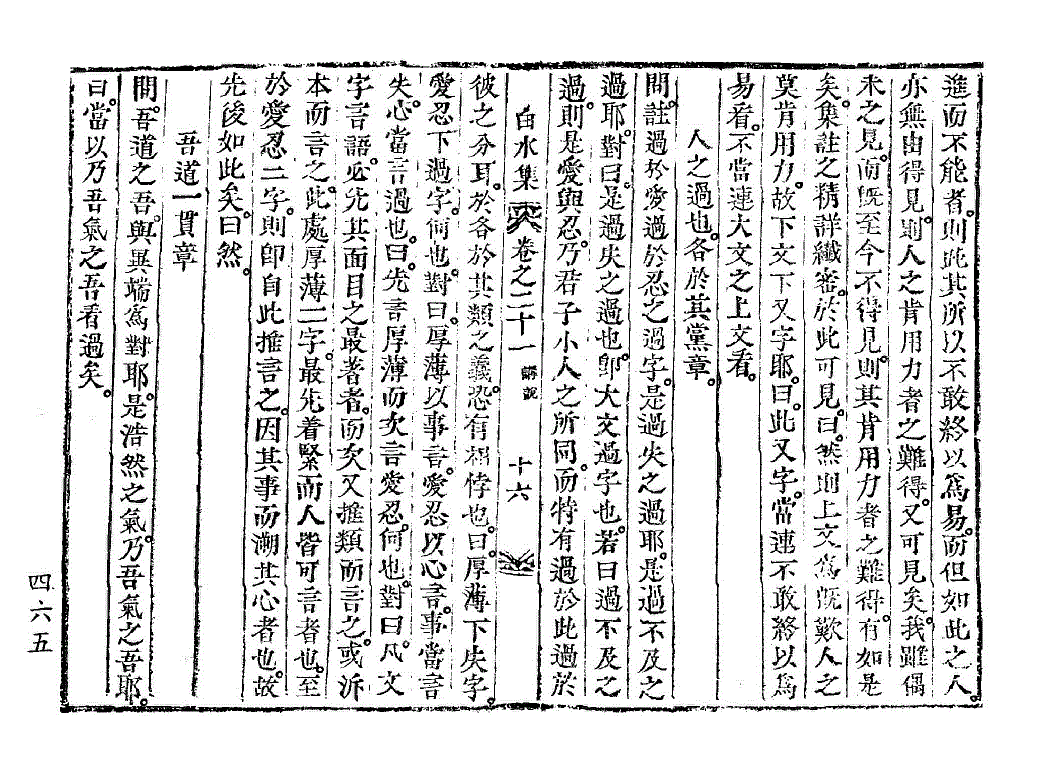 进而不能者。则此其所以不敢终以为易。而但如此之人。亦无由得见。则人之肯用力者之难得。又可见矣。我虽偶未之见。而既至今不得见。则其肯用力者之难得。有如是矣。集注之精详纤密。于此可见。曰。然则上文为既叹人之莫肯用力。故下文下又字耶。曰。此又字。当连不敢终以为易看。不当连大文之上文看。
进而不能者。则此其所以不敢终以为易。而但如此之人。亦无由得见。则人之肯用力者之难得。又可见矣。我虽偶未之见。而既至今不得见。则其肯用力者之难得。有如是矣。集注之精详纤密。于此可见。曰。然则上文为既叹人之莫肯用力。故下文下又字耶。曰。此又字。当连不敢终以为易看。不当连大文之上文看。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章。
问。注过于爱过于忍之过字。是过失之过耶。是过不及之过耶。对曰。是过失之过也。即大文过字也。若曰过不及之过。则是爱与忍。乃君子小人之所同。而特有过于此过于彼之分耳。于各于其类之义。恐有相悖也。曰。厚薄下失字。爱忍下过字。何也。对曰。厚薄以事言。爱忍以心言。事当言失。心当言过也。曰。先言厚薄而次言爱忍。何也。对曰。凡文字言语。必先其面目之最著者。而次又推类而言之。或溯本而言之。此处厚薄二字。最先着紧而人皆可言者也。至于爱忍二字。则即自此推言之。因其事而溯其心者也。故先后如此矣。曰然。
吾道一贯章
问。吾道之吾。与异端为对耶。是浩然之气。乃吾气之吾耶。曰。当以乃吾气之吾看过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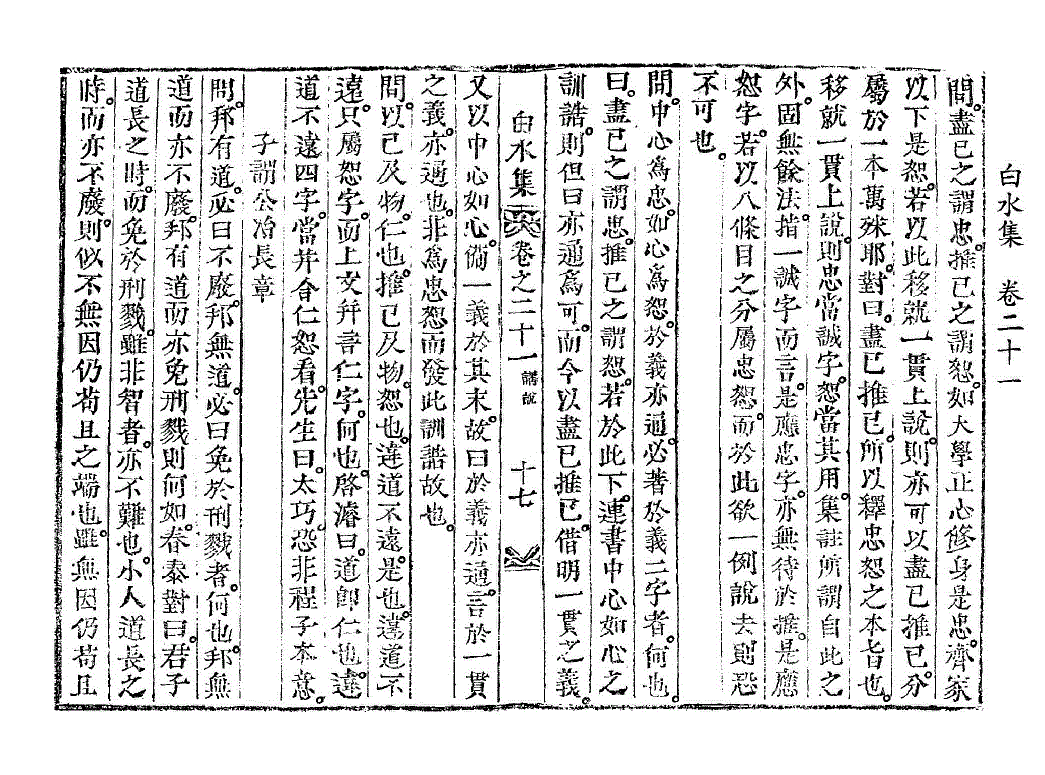 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大学正心修身是忠。齐家以下是恕。若以此移就一贯上说。则亦可以尽己推己。分属于一本万殊耶。对曰。尽己推己。所以释忠恕之本旨也。移就一贯上说。则忠当诚字。恕当其用。集注所谓自此之外。固无馀法。指一诚字而言。是应忠字。亦无待于推。是应恕字。若以八条目之分属忠恕。而于此欲一例说去则恐不可也。
问。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大学正心修身是忠。齐家以下是恕。若以此移就一贯上说。则亦可以尽己推己。分属于一本万殊耶。对曰。尽己推己。所以释忠恕之本旨也。移就一贯上说。则忠当诚字。恕当其用。集注所谓自此之外。固无馀法。指一诚字而言。是应忠字。亦无待于推。是应恕字。若以八条目之分属忠恕。而于此欲一例说去则恐不可也。问。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必著于义二字者。何也。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若于此下。连书中心如心之训诰。则但曰亦通为可。而今以尽己推己。借明一贯之义。又以中心如心。备一义于其末。故曰于义亦通。言于一贯之义。亦通也。非为忠恕而发此训诰故也。
问。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违道不远。只属恕字。而上文并言仁字。何也。启浚曰。道即仁也。违道不远四字。当并合仁恕看。先生曰。太巧。恐非程子本意。
子谓公冶长章
问。邦有道。必曰不废。邦无道。必曰免于刑戮者。何也。邦无道而亦不废。邦有道而亦免刑戮则何如。春泰对曰。君子道长之时。而免于刑戮。虽非智者。亦不难也。小人道长之时。而亦不废。则似不无因仍苟且之端也。虽无因仍苟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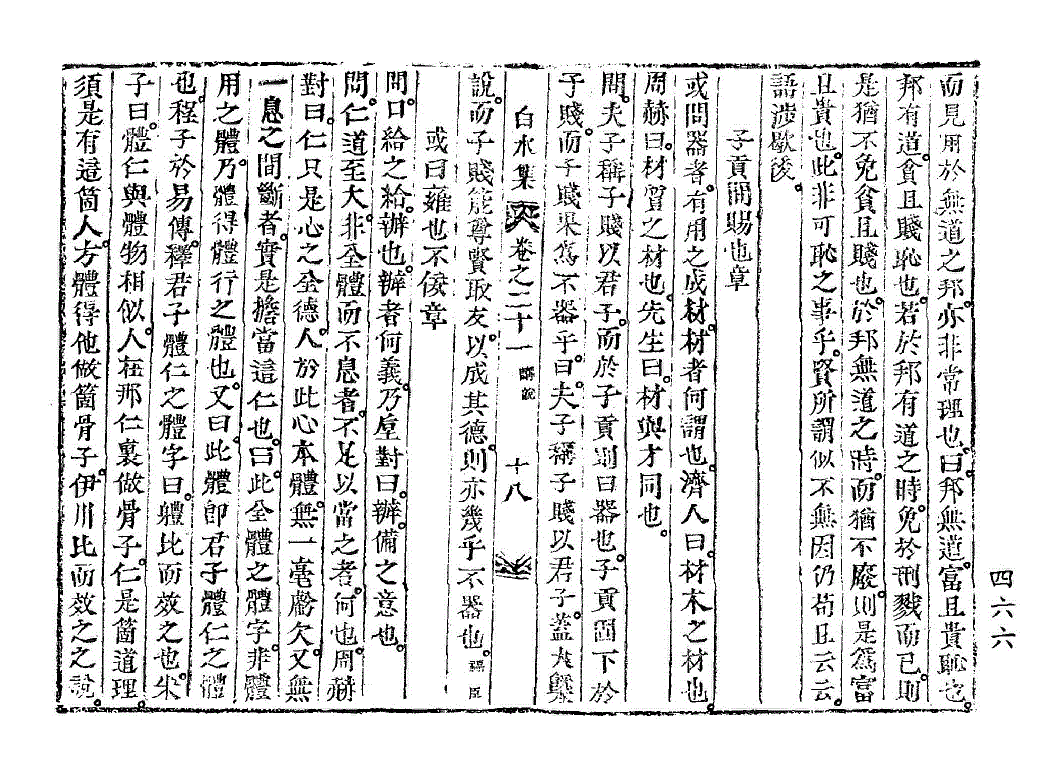 而见用于无道之邦。亦非常理也。曰。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邦有道。贫且贱耻也。若于邦有道之时。免于刑戮而已。则是犹不免贫且贱也。于邦无道之时。而犹不废。则是为富且贵也。此非可耻之事乎。贤所谓似不无因仍苟且云云。语涉歇后。
而见用于无道之邦。亦非常理也。曰。邦无道。富且贵耻也。邦有道。贫且贱耻也。若于邦有道之时。免于刑戮而已。则是犹不免贫且贱也。于邦无道之时。而犹不废。则是为富且贵也。此非可耻之事乎。贤所谓似不无因仍苟且云云。语涉歇后。子贡问赐也章
或问器者。有用之成材。材者何谓也。济人曰。材木之材也。周赫曰。材质之材也。先生曰。材与才同也。
问。夫子称子贱以君子。而于子贡则曰器也。子贡固下于子贱。而子贱果为不器乎。曰。夫子称子贱以君子。盖大槩说。而子贱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则亦几乎不器也。(福臣)
或曰雍也不佞章
问。口给之给。办也。办者何义。乃垕对曰。办。备之意也。
问。仁道至大。非全体而不息者。不足以当之者。何也。周赫对曰。仁只是心之全德。人于此心本体。无一毫亏欠。又无一息之间断者。实是担当这仁也。曰。此全体之体字。非体用之体。乃体得体行之体也。又曰。此体即君子体仁之体也。程子于易传。释君子体仁之体字曰。体比而效之也。朱子曰。体仁与体物相似。人在那仁里做骨子。仁是个道理。须是有这个人。方体得他做个骨子。伊川比而效之之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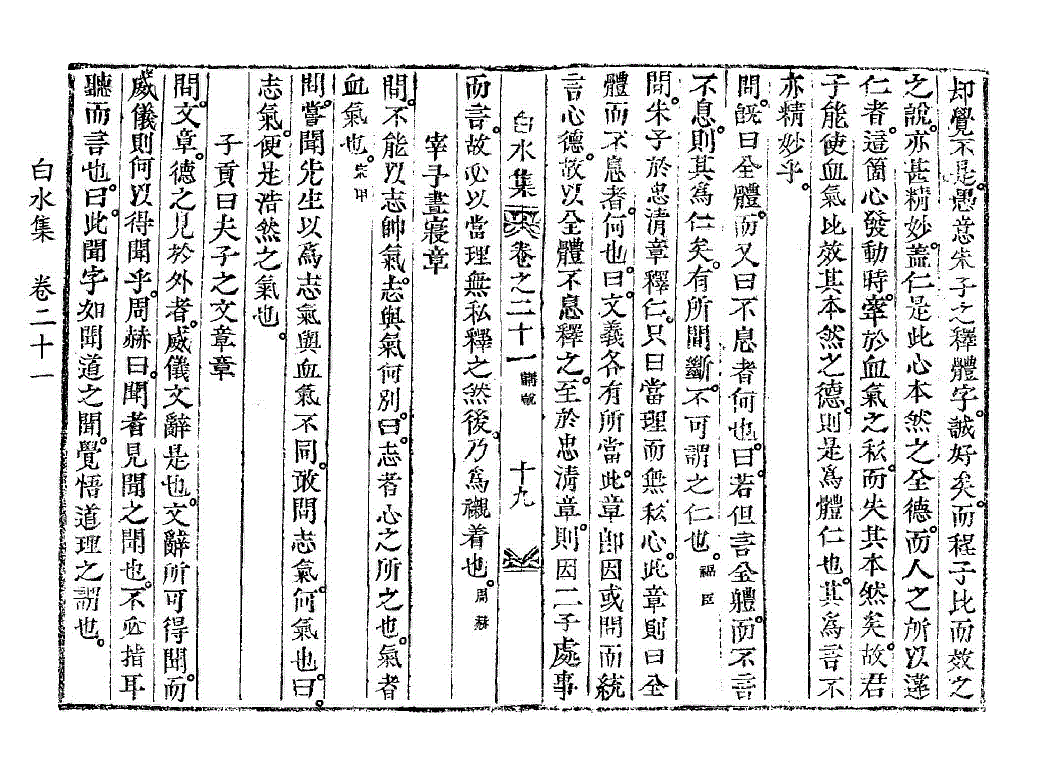 却觉不是。愚意朱子之释体字。诚好矣。而程子比而效之之说。亦甚精妙。盖仁是此心本然之全德。而人之所以违仁者。这个心发动时。牵于血气之私。而失其本然矣。故君子能使血气比效其本然之德。则是为体仁也。其为言不亦精妙乎。
却觉不是。愚意朱子之释体字。诚好矣。而程子比而效之之说。亦甚精妙。盖仁是此心本然之全德。而人之所以违仁者。这个心发动时。牵于血气之私。而失其本然矣。故君子能使血气比效其本然之德。则是为体仁也。其为言不亦精妙乎。问。既曰全体。而又曰不息者何也。曰。若但言全体。而不言不息。则其为仁矣。有所间断。不可谓之仁也。(福臣)
问。朱子于忠清章释仁。只曰当理而无私心。此章则曰全体而不息者。何也。曰。文义各有所当。此章即因或问而统言心德。故以全体不息释之。至于忠清章。则因二子处事而言。故必以当理无私释之然后。乃为衬着也。(周赫)
宰予昼寝章
问。不能以志帅气。志与气何别。曰。志者心之所之也。气者血气也。(宗甲)
问。尝闻先生以为志气与血气不同。敢问志气。何气也。曰。志气。便是浩然之气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章
问。文章。德之见于外者。威仪文辞是也。文辞所可得闻。而威仪则何以得闻乎。周赫曰。闻者见闻之闻也。不必指耳听而言也。曰。此闻字如闻道之闻。觉悟道理之谓也。
子路有闻章
问。子路勇于义而资禀可与有为。又喜闻过则当速改。然而夫子何故恝视其仕卫。而无一言教诲耶。曰。夫子于子将奚先之问。以必也正名答之。则其所教诲之意。至深切矣。而子路不容思量。遽对以有是哉子之迂也。则其不信圣人如此。虽夫子如之何哉。(周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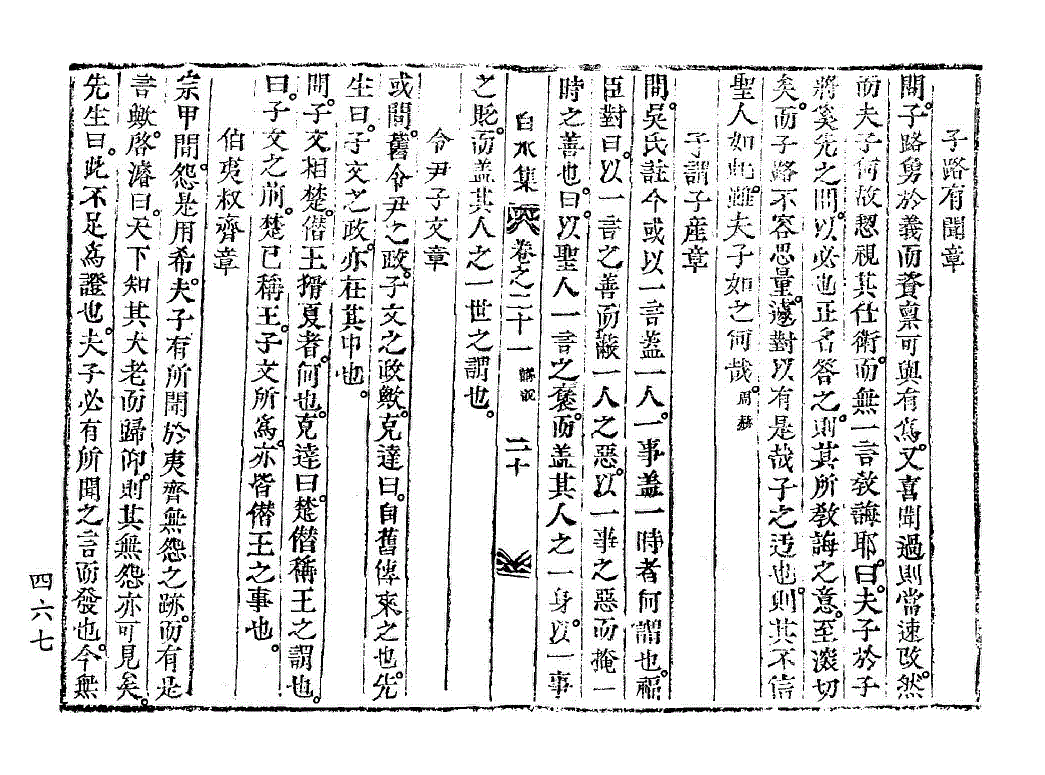 子谓子产章
子谓子产章问。吴氏注今或以一言盖一人。一事盖一时者何谓也。福臣对曰。以一言之善而蔽一人之恶。以一事之恶而掩一时之善也。曰。以圣人一言之褒。而盖其人之一身。以一事之贬。而盖其人之一世之谓也。
令尹子文章
或问。旧令尹之政。子文之政欤。克达曰。自旧传来之也。先生曰。子文之政。亦在其中也。
问。子文相楚。僭王猾夏者。何也。克达曰。楚僭称王之谓也。曰。子文之前。楚已称王。子文所为。亦皆僭王之事也。
伯夷叔齐章
宗甲问。怨是用希。夫子有所闻于夷齐无怨之迹。而有是言欤。启浚曰。天下知其大老而归仰。则其无怨亦可见矣。先生曰。此不足为證也。夫子必有所闻之言而发也。今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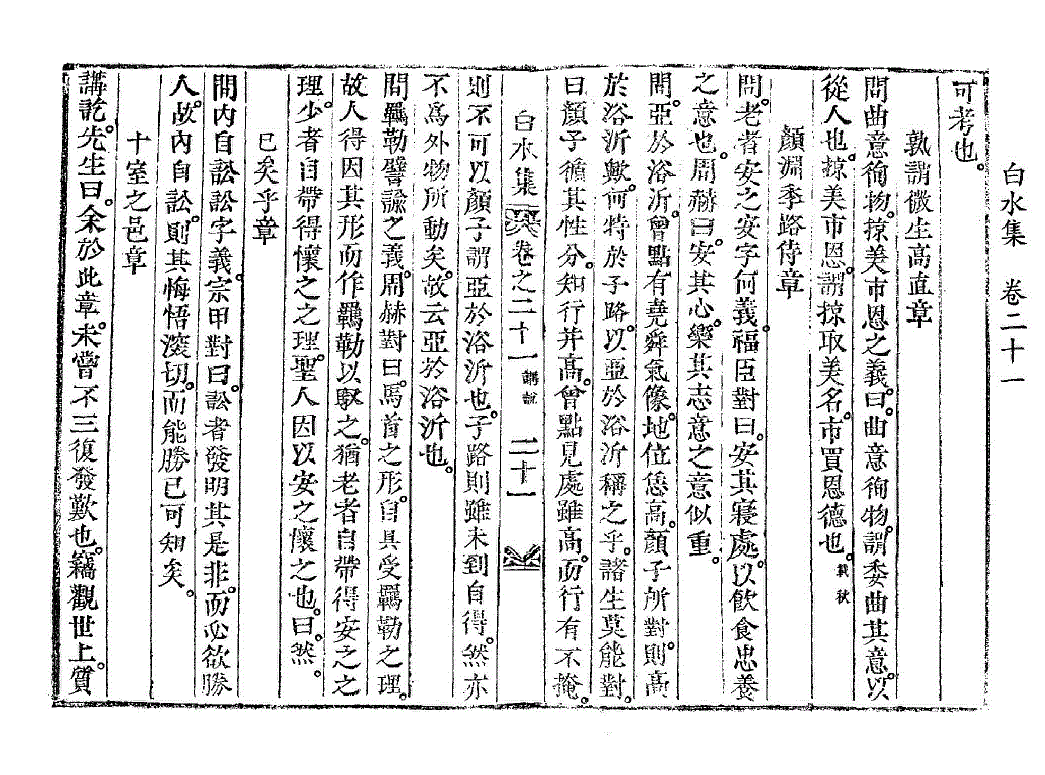 可考也。
可考也。孰谓微生高直章
问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之义。曰。曲意徇物。谓委曲其意。以从人也。掠美市恩。谓掠取美名。市买恩德也。(载秋)
颜渊季路侍章
问。老者安之安字何义。福臣对曰。安其寝处。以饮食忠养之意也。周赫曰。安其心。乐其志意之意似重。
问。亚于浴沂。曾点有尧舜气像。地位恁高。颜子所对。则高于浴沂欤。何特于子路。以亚于浴沂称之乎。诸生莫能对。曰颜子循其性分。知行并高。曾点见处虽高。而行有不掩。则不可以颜子谓亚于浴沂也。子路则虽未到自得。然亦不为外物所动矣。故云亚于浴沂也。
问羁勒譬谕之义。周赫对曰。马首之形。自具受羁勒之理。故人得因其形而作羁勒以驭之。犹老者自带得安之之理。少者自带得怀之之理。圣人因以安之怀之也。曰。然。
已矣乎章
问内自讼讼字义。宗甲对曰。讼者发明其是非。而必欲胜人。故内自讼。则其悔悟深切。而能胜己可知矣。
十室之邑章
讲讫。先生曰。余于此章。未尝不三复发叹也。窃观世上。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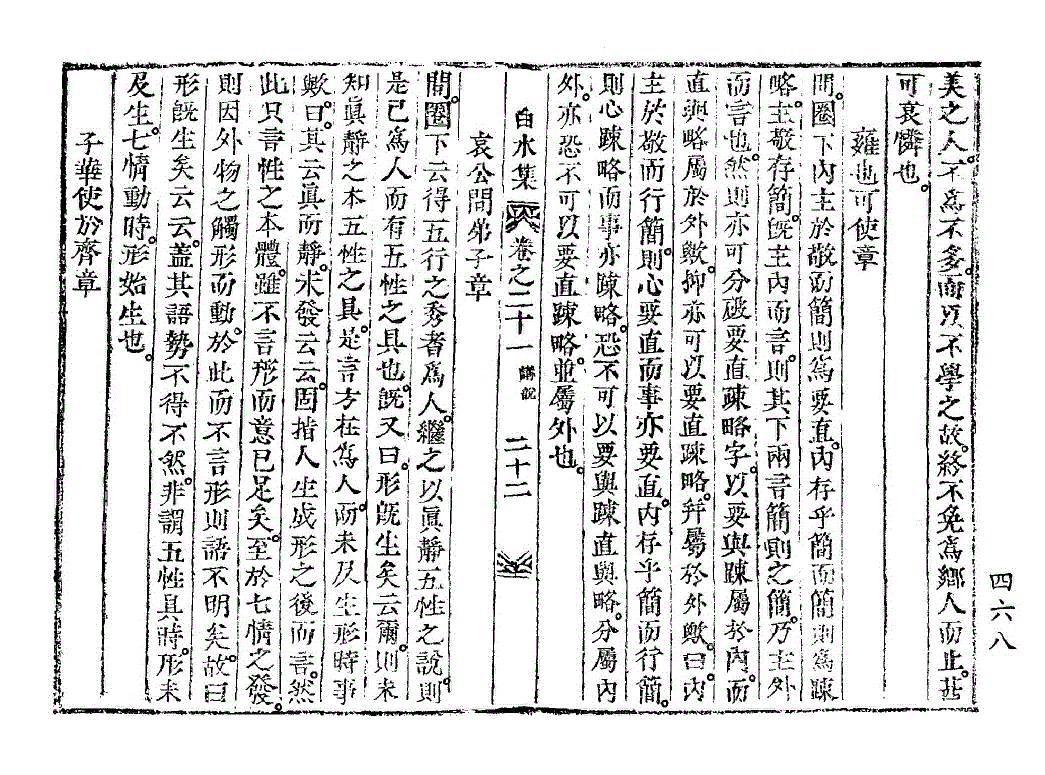 美之人。不为不多。而以不学之故。终不免为乡人而止。甚可哀怜也。
美之人。不为不多。而以不学之故。终不免为乡人而止。甚可哀怜也。雍也可使章
问。圈下内主于敬而简则为要直。内存乎简而简则为疏略。主敬存简。既主内而言。则其下两言简则之简。乃主外而言也。然则亦可分破要直疏略字。以要与疏属于内。而直与略属于外欤。抑亦可以要直疏略。并属于外欤。曰。内主于敬而行简。则心要直而事亦要直。内存乎简而行简。则心疏略而事亦疏略。恐不可以要与疏直与略。分属内外。亦恐不可以要直疏略。并属外也。
哀公问弟子章
问。圈下云得五行之秀者为人。继之以真静五性之说。则是已为人而有五性之具也。既又曰。形既生矣云尔。则未知真静之本五性之具。是言方在为人。而未及生形时事欤。曰。其云真而静。未发云云。固指人生成形之后而言。然此只言性之本体。虽不言形而意已足矣。至于七情之发。则因外物之触形而动。于此而不言形则语不明矣。故曰形既生矣云云。盖其语势不得不然。非谓五性具时。形未及生。七情动时。形始生也。
子华使于齐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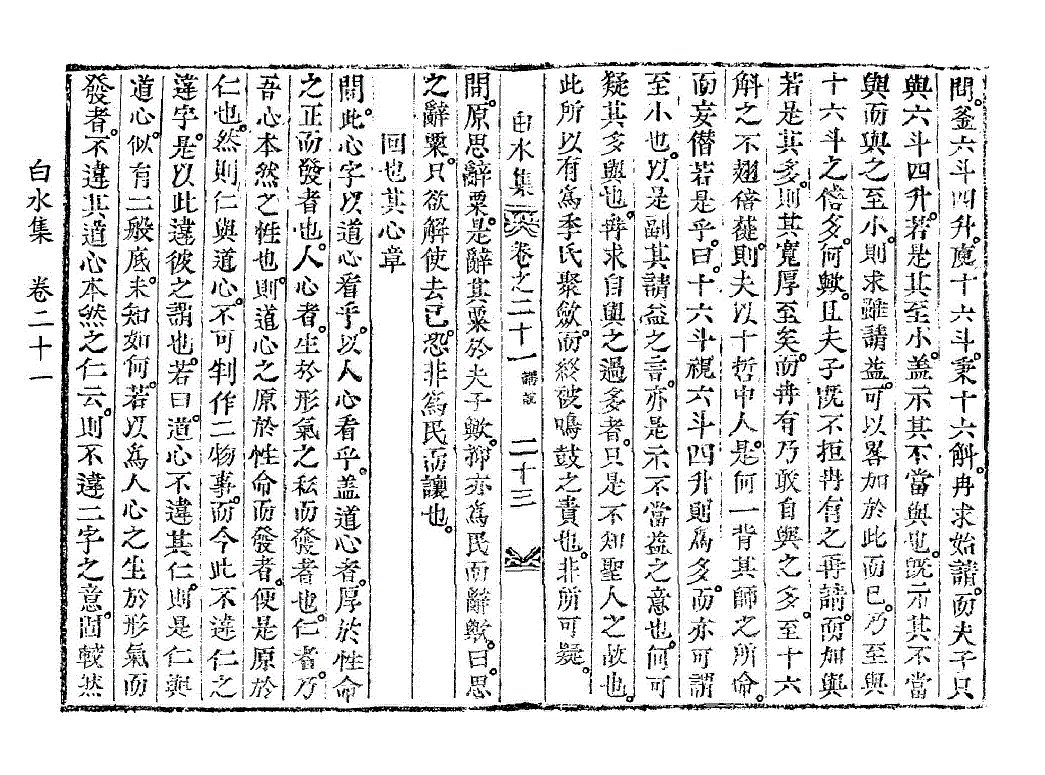 问。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冉求始请。而夫子只与六斗四升。若是其至小。盖示其不当与也。既示其不当与而与之至小。则求虽请益。可以略加于此而已。乃至与十六斗之倍多。何欤。且夫子既不拒冉有之再请。而加与若是其多。则其宽厚至矣。而冉有乃敢自与之多。至十六斛之不翅倍蓰。则夫以十哲中人。是何一背其师之所命。而妄僭若是乎。曰。十六斗视六斗四升则为多。而亦可谓至小也。以是副其请益之言。亦是示不当益之意也。何可疑其多与也。冉求自与之过多者。只是不知圣人之故也。此所以有为季氏聚敛。而终被鸣鼓之责也。非所可疑。
问。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冉求始请。而夫子只与六斗四升。若是其至小。盖示其不当与也。既示其不当与而与之至小。则求虽请益。可以略加于此而已。乃至与十六斗之倍多。何欤。且夫子既不拒冉有之再请。而加与若是其多。则其宽厚至矣。而冉有乃敢自与之多。至十六斛之不翅倍蓰。则夫以十哲中人。是何一背其师之所命。而妄僭若是乎。曰。十六斗视六斗四升则为多。而亦可谓至小也。以是副其请益之言。亦是示不当益之意也。何可疑其多与也。冉求自与之过多者。只是不知圣人之故也。此所以有为季氏聚敛。而终被鸣鼓之责也。非所可疑。问。原思辞粟。是辞其粟于夫子欤。抑亦为民而辞欤。曰。思之辞粟。只欲解使去已。恐非为民而让也。
回也其心章
问。此心字以道心看乎。以人心看乎。盖道心者。厚于性命之正而发者也。人心者。生于形气之私而发者也。仁者。乃吾心本然之性也。则道心之原于性命而发者。便是原于仁也。然则仁与道心。不可判作二物事。而今此不违仁之违字。是以此违彼之谓也。若曰。道心不违其仁。则是仁与道心。似有二般底。未知如何。若以为人心之生于形气而发者。不违其道心本然之仁云。则不违二字之意。固较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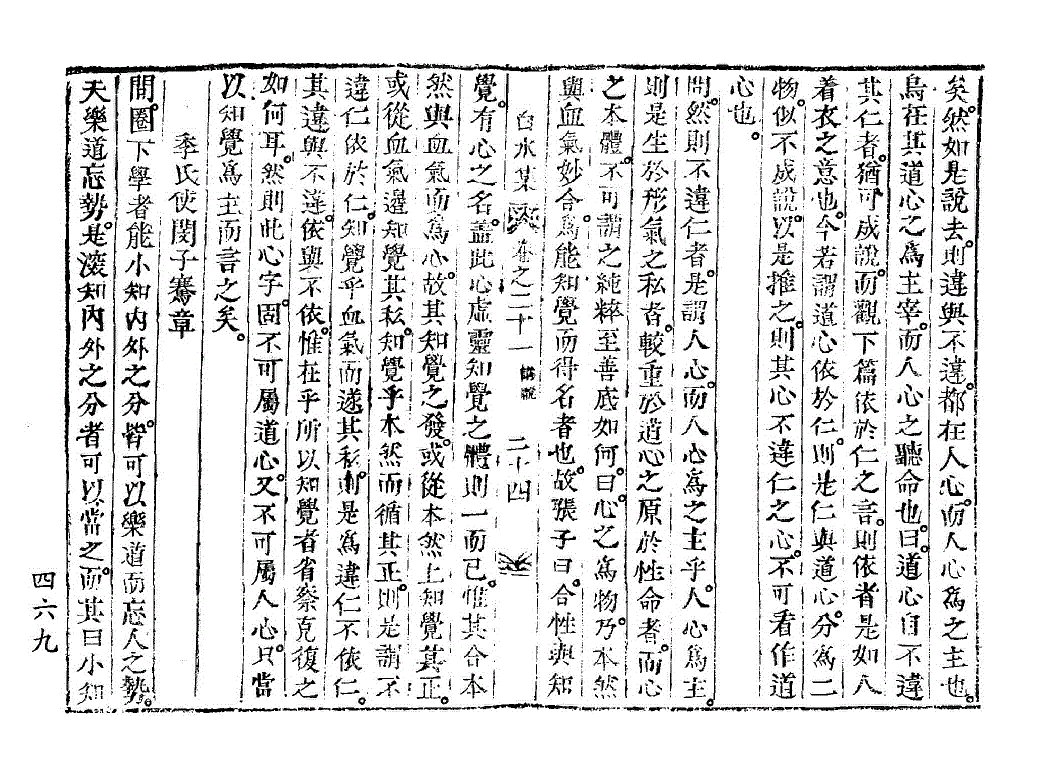 矣。然如是说去。则违与不违。都在人心。而人心为之主也。乌在其道心之为主宰。而人心之听命也。曰。道心自不违其仁者。犹可成说。而观下篇依于仁之言。则依者是如人着衣之意也。今若谓道心依于仁。则是仁与道心。分为二物。似不成说。以是推之。则其心不违仁之心。不可看作道心也。
矣。然如是说去。则违与不违。都在人心。而人心为之主也。乌在其道心之为主宰。而人心之听命也。曰。道心自不违其仁者。犹可成说。而观下篇依于仁之言。则依者是如人着衣之意也。今若谓道心依于仁。则是仁与道心。分为二物。似不成说。以是推之。则其心不违仁之心。不可看作道心也。问。然则不违仁者。是谓人心。而人心为之主乎。人心为主。则是生于形气之私者。较重于道心之原于性命者。而心之本体。不可谓之纯粹至善底如何。曰。心之为物。乃本然与血气妙合。为能知觉而得名者也。故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盖此心虚灵知觉之体则一而已。惟其合本然与血气而为心。故其知觉之发。或从本然上知觉其正。或从血气边知觉其私。知觉乎本然而循其正。则是谓不违仁依于仁。知觉乎血气而遂其私。则是为违仁不依仁。其违与不违。依与不依。惟在乎所以知觉者省察克复之如何耳。然则此心字。固不可属道心。又不可属人心。只当以知觉为主而言之矣。
季氏使闵子骞章
问。圈下学者能小知内外之分。皆可以乐道而忘人之势。天乐道忘势。是深知内外之分者可以当之。而其曰小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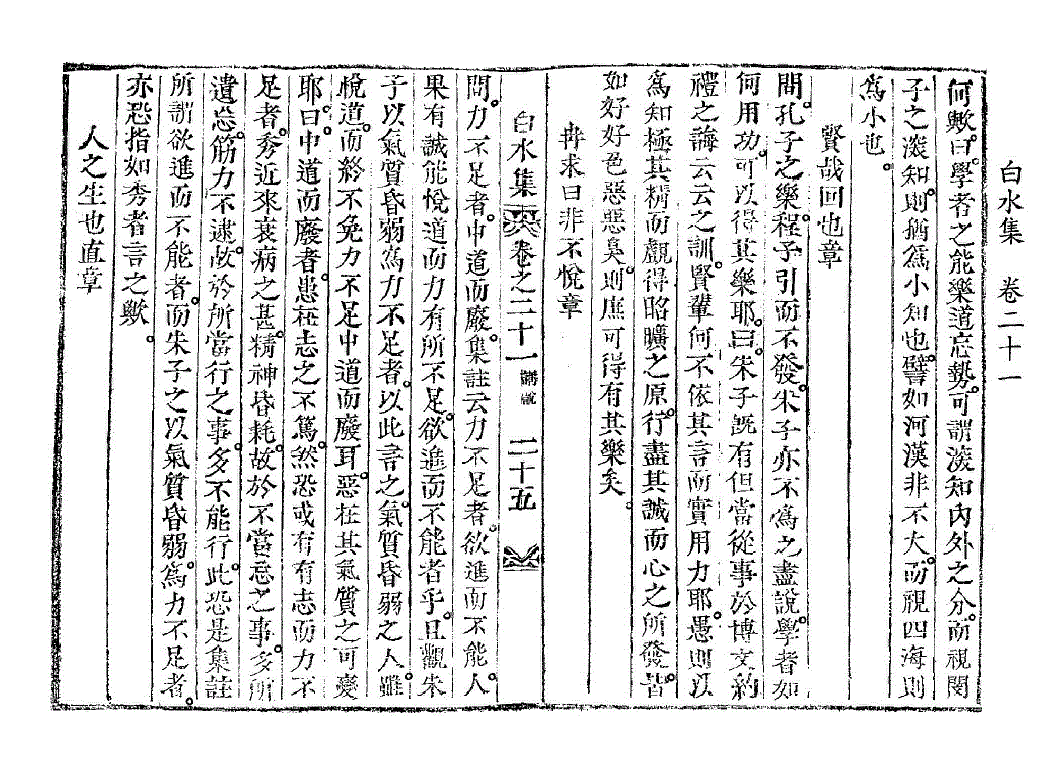 何欤。曰。学者之能乐道忘势。可谓深知内外之分。而视闵子之深知。则犹为小知也。譬如河汉非不大。而视四海则为小也。
何欤。曰。学者之能乐道忘势。可谓深知内外之分。而视闵子之深知。则犹为小知也。譬如河汉非不大。而视四海则为小也。贤哉回也章
问。孔子之乐。程子引而不发。朱子亦不为之尽说。学者如何用功。可以得其乐耶。曰。朱子既有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云云之训。贤辈何不依其言而实用力耶。愚则以为知极其精而觑得昭旷之原。行尽其诚而心之所发。皆如好好色恶恶臭。则庶可得有其乐矣。
冉求曰非不悦章
问。力不足者。中道而废。集注云力不足者。欲进而不能。人果有诚能悦道而力有所不足。欲进而不能者乎。且观朱子以气质昏弱为力不足者。以此言之。气质昏弱之人。虽悦道。而终不免力不足中道而废耳。恶在其气质之可变耶。曰。中道而废者。患在志之不笃。然恐或有有志而力不足者。秀近来衰病之甚。精神昏耗。故于不当忘之事。多所遗忘。筋力不逮。故于所当行之事。多不能行。此恐是集注所谓欲进而不能者。而朱子之以气质昏弱。为力不足者。亦恐指如秀者言之欤。
人之生也直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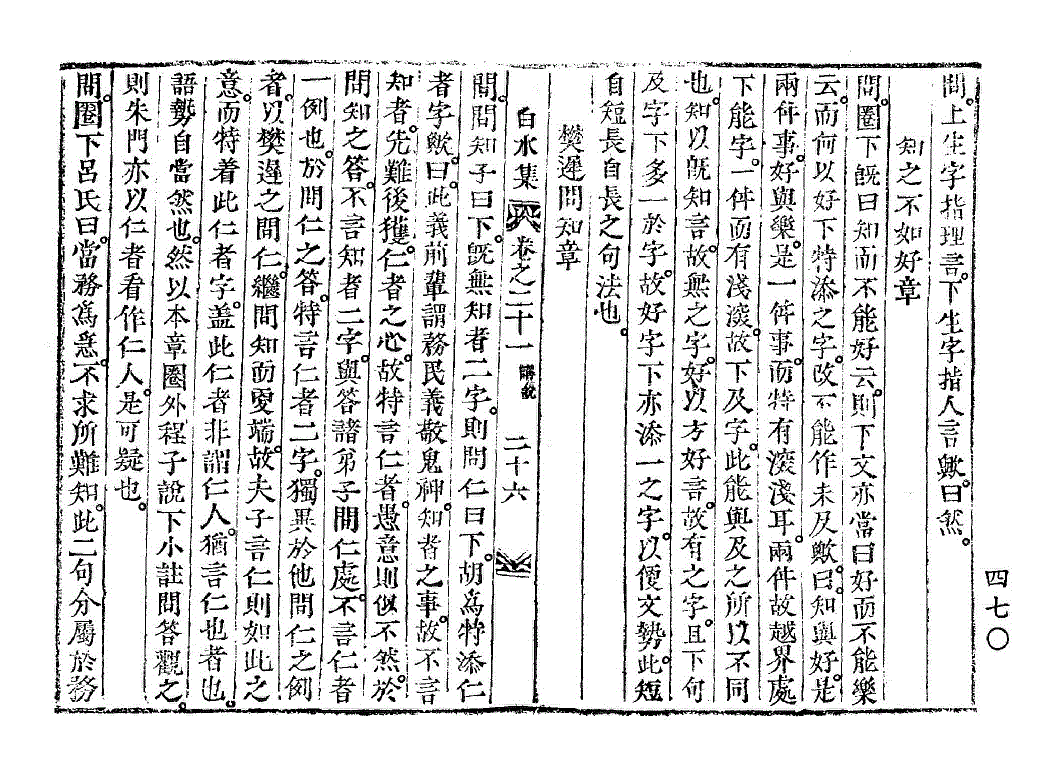 问。上生字指理言。下生字指人言欤。曰然。
问。上生字指理言。下生字指人言欤。曰然。知之不如好章
问。圈下既曰知而不能好云。则下文亦当曰好而不能乐云。而何以好下特添之字。改不能作未及欤。曰。知与好。是两件事。好与乐。是一件事。而特有深浅耳。两件故越界处下能字。一件而有浅深。故下及字。此能与及之所以不同也。知以既知言。故无之字。好以方好言。故有之字。且下句及字下多一于字。故好字下亦添一之字。以便文势。此短自短长自长之句法也。
樊迟问知章
问。问知子曰下。既无知者二字。则问仁曰下。胡为特添仁者字欤。曰。此义前辈谓务民义敬鬼神。知者之事。故不言知者。先难后获。仁者之心。故特言仁者。愚意则似不然。于问知之答。不言知者二字。与答诸弟子问仁处。不言仁者一例也。于问仁之答。特言仁者二字。独异于他问仁之例者。以樊迟之问仁。继问知而更端。故夫子言仁则如此之意。而特着此仁者字。盖此仁者非谓仁人。犹言仁也者也。语势自当然也。然以本章圈外程子说下小注问答观之。则朱门亦以仁者看作仁人。是可疑也。
问。圈下吕氏曰。当务为急。不求所难知。此二句分属于务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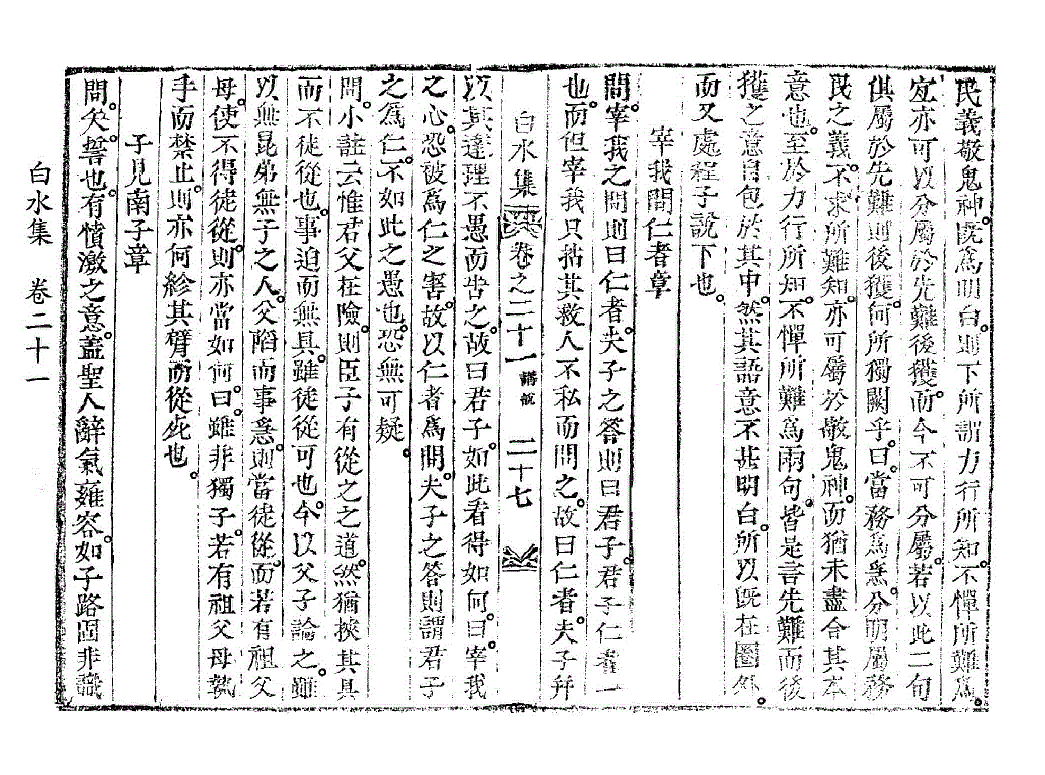 民义敬鬼神。既为明白。则下所谓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宜亦可以分属于先难后获。而今不可分属。若以此二句俱属于先难则后获。何所独阙乎。曰。当务为急。分明属务民之义。不求所难知。亦可属于敬鬼神。而犹未尽合其本意也。至于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两句。皆是言先难而后获之意自包于其中。然其语意不甚明白。所以既在圈外。而又处程子说下也。
民义敬鬼神。既为明白。则下所谓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宜亦可以分属于先难后获。而今不可分属。若以此二句俱属于先难则后获。何所独阙乎。曰。当务为急。分明属务民之义。不求所难知。亦可属于敬鬼神。而犹未尽合其本意也。至于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两句。皆是言先难而后获之意自包于其中。然其语意不甚明白。所以既在圈外。而又处程子说下也。宰我问仁者章
问。宰我之问则曰仁者。夫子之答则曰君子。君子仁者一也。而但宰我只拈其救人不私而问之。故曰仁者。夫子并以其达理不愚而告之。故曰君子。如此看得如何。曰。宰我之心。恐被为仁之害。故以仁者为问。夫子之答则谓君子之为仁。不如此之愚也。恐无可疑。
问。小注云惟君父在险。则臣子有从之之道。然犹挟其具而不徒从也。事迫而无具。虽徒从可也。今以父子论之。虽以无昆弟无子之人。父陷而事急。则当徒从。而若有祖父母。使不得徒从。则亦当如何。曰。虽非独子。若有祖父母执手而禁止。则亦何紾其臂而从死也。
子见南子章
问。矢。誓也。有愤激之意。盖圣人辞气雍容。如子路固非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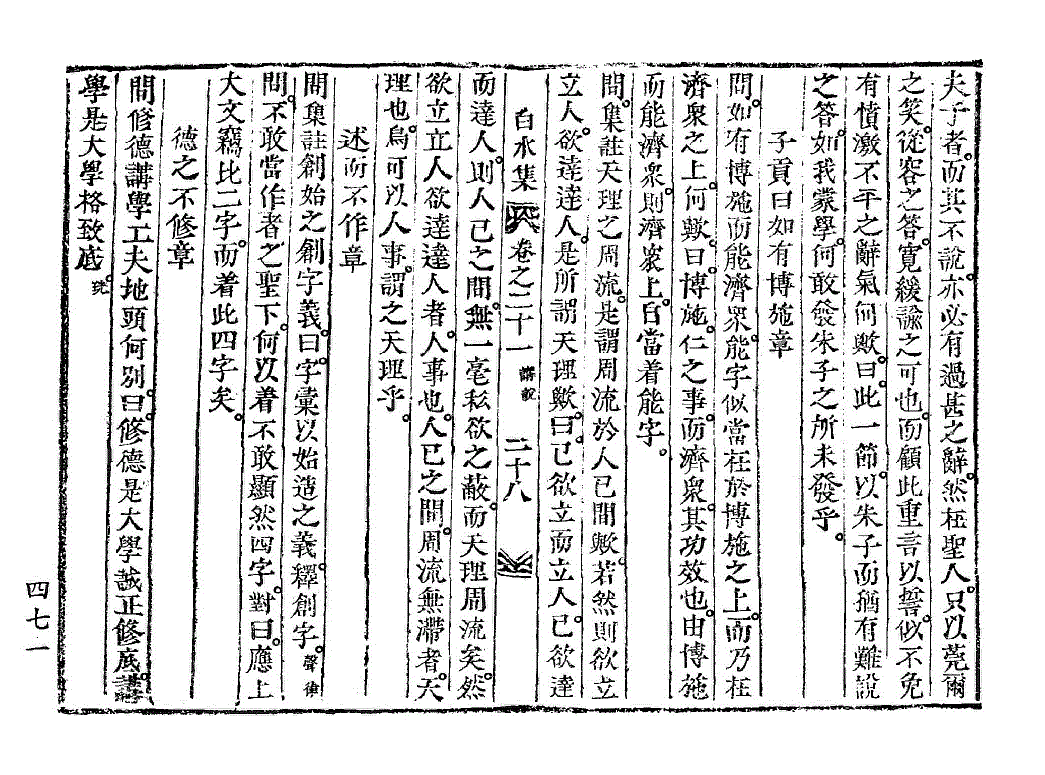 夫子者。而其不说。亦必有过甚之辞。然在圣人。只以莞尔之笑。从容之答。宽缓谕之可也。而顾此重言以誓。似不免有愤激不平之辞气何欤。曰。此一节。以朱子而犹有难说之答。如我蒙学。何敢发朱子之所未发乎。
夫子者。而其不说。亦必有过甚之辞。然在圣人。只以莞尔之笑。从容之答。宽缓谕之可也。而顾此重言以誓。似不免有愤激不平之辞气何欤。曰。此一节。以朱子而犹有难说之答。如我蒙学。何敢发朱子之所未发乎。子贡曰如有博施章
问。如有博施而能济众。能字似当在于博施之上。而乃在济众之上。何欤。曰。博施。仁之事。而济众。其功效也。由博施而能济众。则济众上。自当着能字。
问。集注天理之周流。是谓周流于人己间欤。若然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所谓天理欤。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人己之问(一作间)。无一毫私欲之蔽。而天理周流矣。然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者。人事也。人己之间。周流无滞者。天理也。乌可以人事。谓之天理乎。
述而不作章
问集注创始之创字义。曰。字汇以始造之义。释创字。(声律)
问。不敢当作者之圣下。何以着不敢显然四字。对曰。应上大文窃比二字。而着此四字矣。
德之不修章
问修德讲学工夫地头何别。曰。修德是大学诚正修底。讲学是大学格致底。(珖)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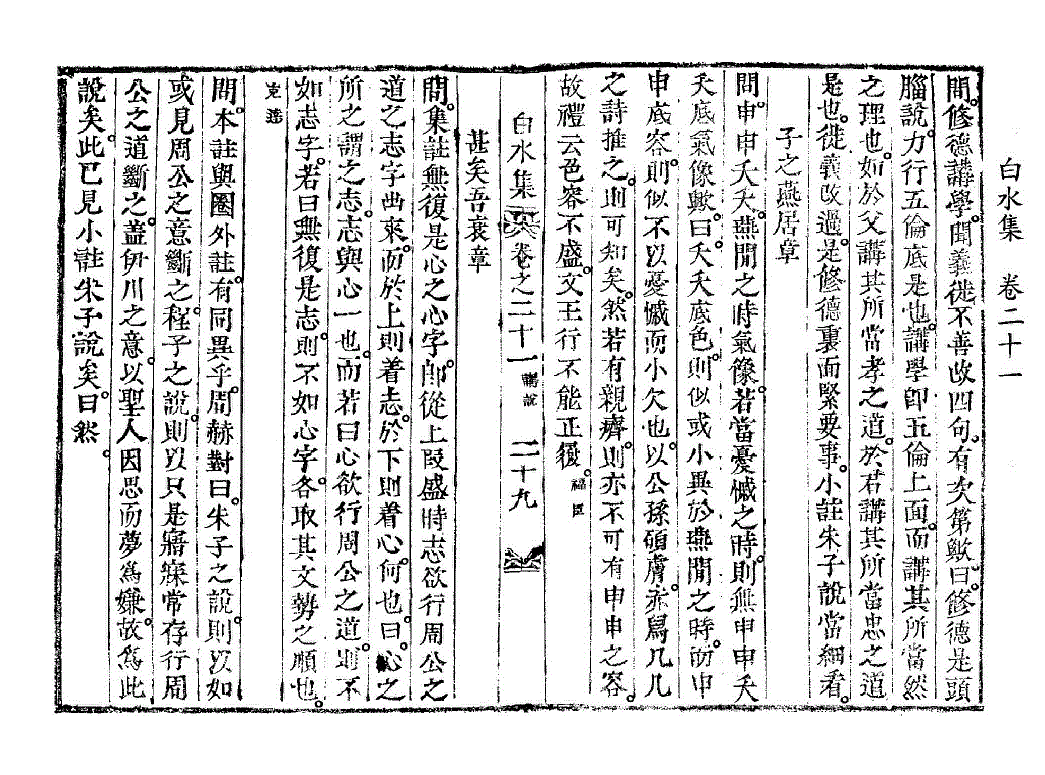 问。修德讲学。闻义徙不善改四句。有次第欤。曰。修德是头脑说。力行五伦底是也。讲学即五伦上面。而讲其所当然之理也。如于父讲其所当孝之道。于君讲其所当忠之道是也。徙义改过。是修德里面紧要事。小注朱子说当细看。
问。修德讲学。闻义徙不善改四句。有次第欤。曰。修德是头脑说。力行五伦底是也。讲学即五伦上面。而讲其所当然之理也。如于父讲其所当孝之道。于君讲其所当忠之道是也。徙义改过。是修德里面紧要事。小注朱子说当细看。子之燕居章
问。申申夭夭。燕閒之时气像。若当忧戚之时。则无申申夭夭底气像欤。曰。夭夭底色。则似或小异于燕閒之时。而申申底容。则似不以忧戚而小欠也。以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之诗推之。则可知矣。然若有亲癠。则亦不可有申申之容。故礼云色容不盛。文王行不能正履。(福臣)
甚矣吾衰章
问。集注无复是心之心字。即从上段盛时志欲行周公之道之志字出来。而于上则着志。于下则着心。何也。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志与心一也。而若曰心欲行周公之道。则不如志字。若曰无复是志。则不如心字。各取其文势之顺也。(克达)
问。本注与圈外注。有同异乎。周赫对曰。朱子之说。则以如或见周公之意断之。程子之说。则以只是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断之。盖伊川之意。以圣人因思而梦为嫌。故为此说矣。此已见小注朱子说矣。曰然。
志于道章
问。据字与依字义。有轻重浅深之可言欤。曰。据如手执物而固守之。依如身着衣而不离也。依之意视据之意。深一节矣。(周赫)
问。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兼包五性者。则恐明德亦不出于仁欤。曰。仁与明德。俱是本心之德。而所指地头不同。此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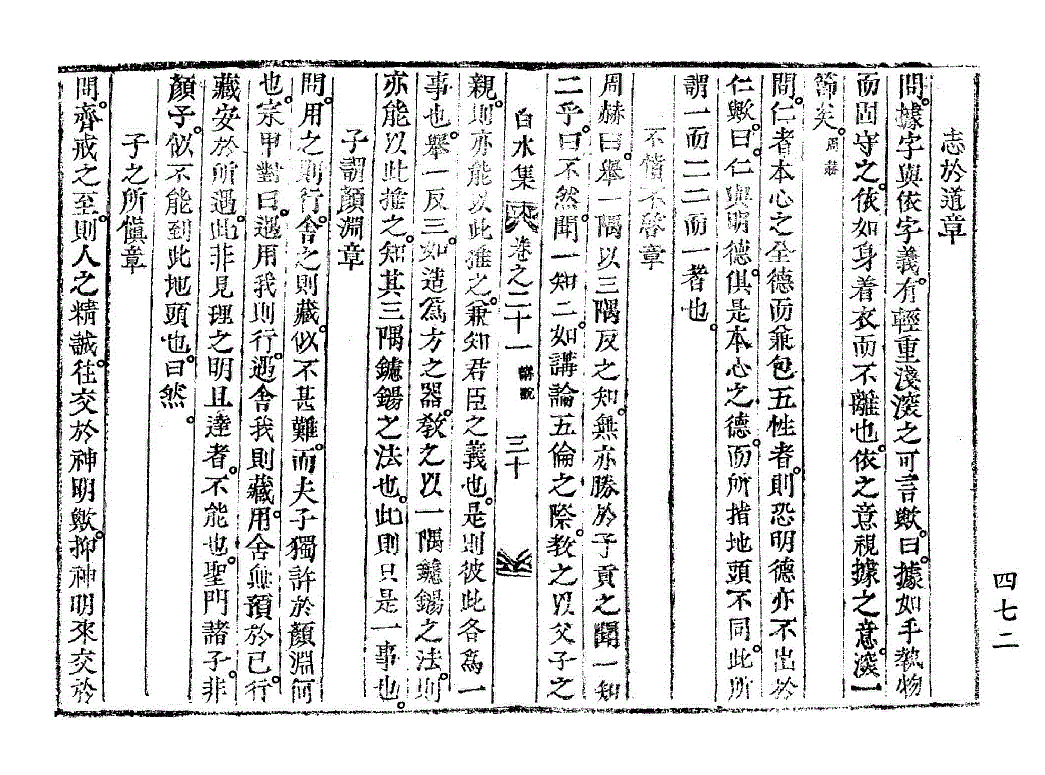 不愤不启章
不愤不启章周赫曰。举一隅以三隅反之知。无亦胜于子贡之闻一知二乎。曰不然。闻一知二。如讲论五伦之际。教之以父子之亲。则亦能以此推之。兼知君臣之义也。是则彼此各为一事也。举一反三。如造为方之器。教之以一隅铝铴之法。则亦能以此推之。知其三隅铝铴之法也。此则只是一事也。
子谓颜渊章
问。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似不甚难。而夫子独许于颜渊何也。宗甲对曰。遇用我则行。遇舍我则藏。用舍无预于己。行藏安于所遇。此非见理之明且达者。不能也。圣门诸子。非颜子。似不能到此地头也。曰然。
子之所慎章
问。齐戒之至。则人之精诚。往交于神明欤。抑神明来交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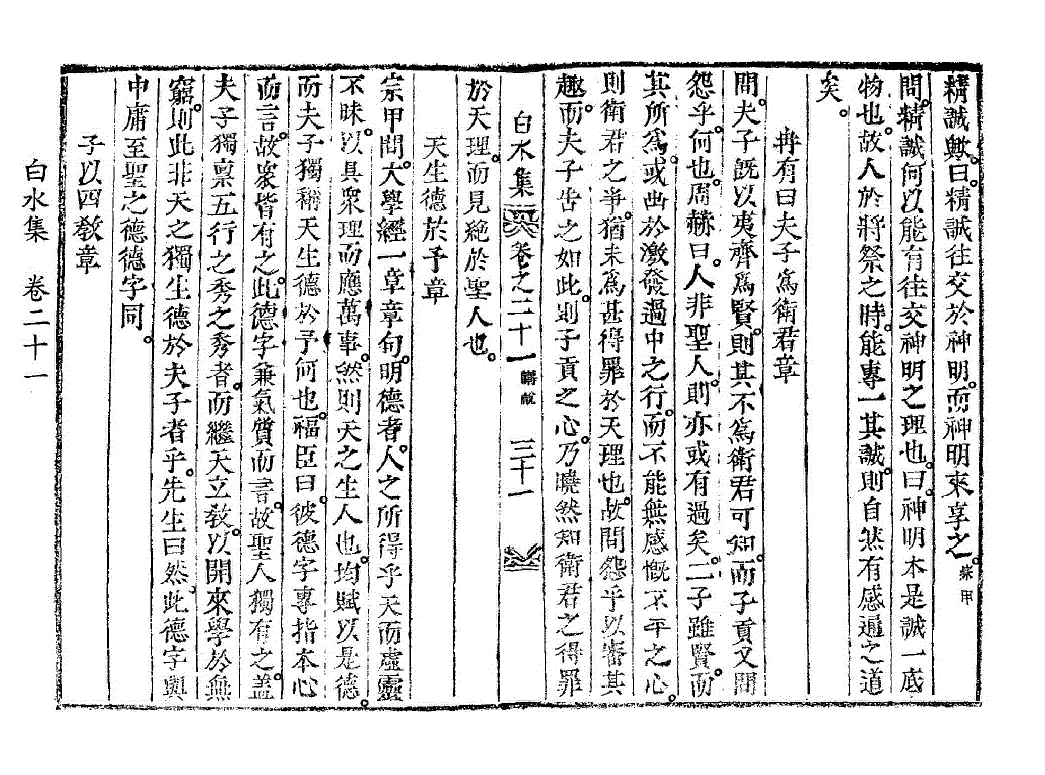 精诚欤。曰。精诚往交于神明。而神明来享之。(宗甲)
精诚欤。曰。精诚往交于神明。而神明来享之。(宗甲)问。精诚何以能有往交神明之理也。曰。神明本是诚一底物也。故人于将祭之时。能专一其诚。则自然有感通之道矣。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章
问。夫子既以夷齐为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而子贡又问怨乎。何也。周赫曰。人非圣人。则亦或有过矣。二子虽贤。而其所为。或出于激发过中之行。而不能无感慨不平之心。则卫君之争。犹未为甚得罪于天理也。故问怨乎以审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则子贡之心。乃晓然知卫君之得罪于天理。而见绝于圣人也。
天生德于予章
宗甲问。大学经一章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然则天之生人也。均赋以是德。而夫子独称天生德于予何也。福臣曰。彼德字专指本心而言。故众皆有之。此德字兼气质而言。故圣人独有之。盖夫子独禀五行之秀之秀者。而继天立教。以开来学于无穷。则此非天之独生德于夫子者乎。先生曰然。此德字与中庸至圣之德德字同。
子以四教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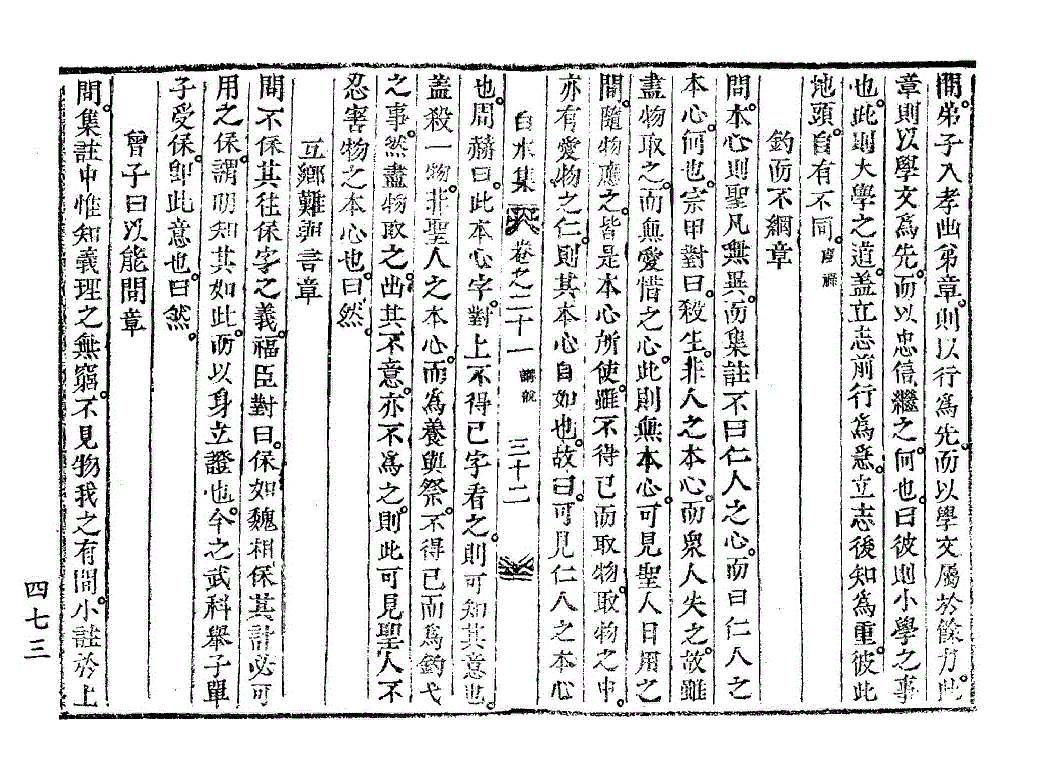 问。弟子入孝出弟章。则以行为先。而以学文属于馀力。此章则以学文为先。而以忠信继之。何也。曰彼则小学之事也。此则大学之道。盖立志前行为急。立志后知为重。彼此地头。自有不同。(庆禄)
问。弟子入孝出弟章。则以行为先。而以学文属于馀力。此章则以学文为先。而以忠信继之。何也。曰彼则小学之事也。此则大学之道。盖立志前行为急。立志后知为重。彼此地头。自有不同。(庆禄)钓而不网章
问。本心则圣凡无异。而集注不曰仁人之心。而曰仁人之本心。何也。宗甲对曰。杀生。非人之本心。而众人失之。故虽尽物取之。而无爱惜之心。此则无本心。可见圣人日用之间。随物应之。皆是本心所使。虽不得已而取物。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则其本心自如也。故曰。可见仁人之本心也。周赫曰。此本心字。对上不得已字看之。则可知其意也。盖杀一物。非圣人之本心。而为养与祭。不得已而为钓弋之事。然尽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为之。则此可见圣人不忍害物之本心也。曰然。
互乡难与言章
问不保其往保字之义。福臣对曰。保如魏相。保其计必可用之保。谓明知其如此。而以身立證也。今之武科举子单子受保。即此意也。曰然。
曾子曰以能问章
问。集注中惟知义理之无穷。不见物我之有间。小注于上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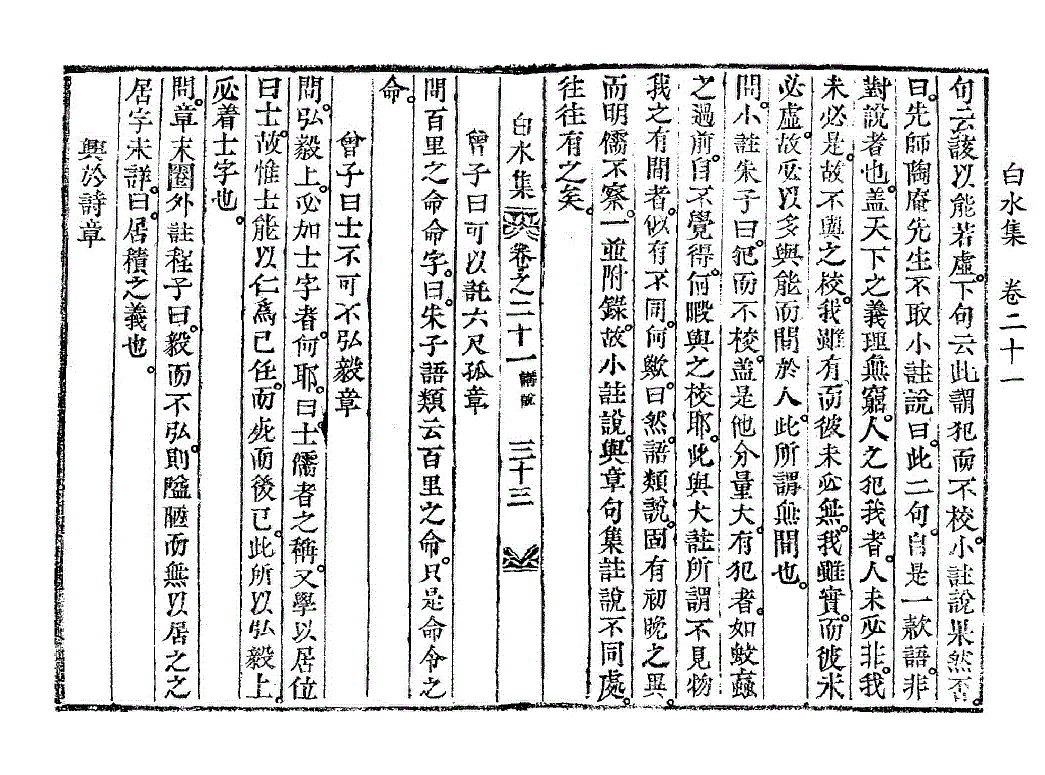 句云该以能若虚。下句云此谓犯而不校。小注说果然否。曰。先师陶庵先生不取小注说曰。此二句。自是一款语。非对说者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人之犯我者。人未必非。我未必是。故不与之校。我虽有。而彼未必无。我虽实。而彼未必虚。故必以多与能而问于人。此所谓无间也。
句云该以能若虚。下句云此谓犯而不校。小注说果然否。曰。先师陶庵先生不取小注说曰。此二句。自是一款语。非对说者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人之犯我者。人未必非。我未必是。故不与之校。我虽有。而彼未必无。我虽实。而彼未必虚。故必以多与能而问于人。此所谓无间也。问。小注朱子曰。犯而不校。盖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虻之过前。自不觉得。何暇与之校耶。此与大注所谓不见物我之有间者。似有不同。何欤。曰然。语类说。固有初晚之异。而明儒不察。一并附录。故小注说。与章句集注说不同处。往往有之矣。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孤章
问百里之命命字。曰。朱子语类云百里之命。只是命令之命。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章
问。弘毅上。必加士字者。何耶。曰。士儒者之称。又学以居位曰士。故惟士能以仁为己任。而死而后已。此所以弘毅上。必着士字也。
问。章末圈外注程子曰。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之居字未详。曰。居积之义也。
兴于诗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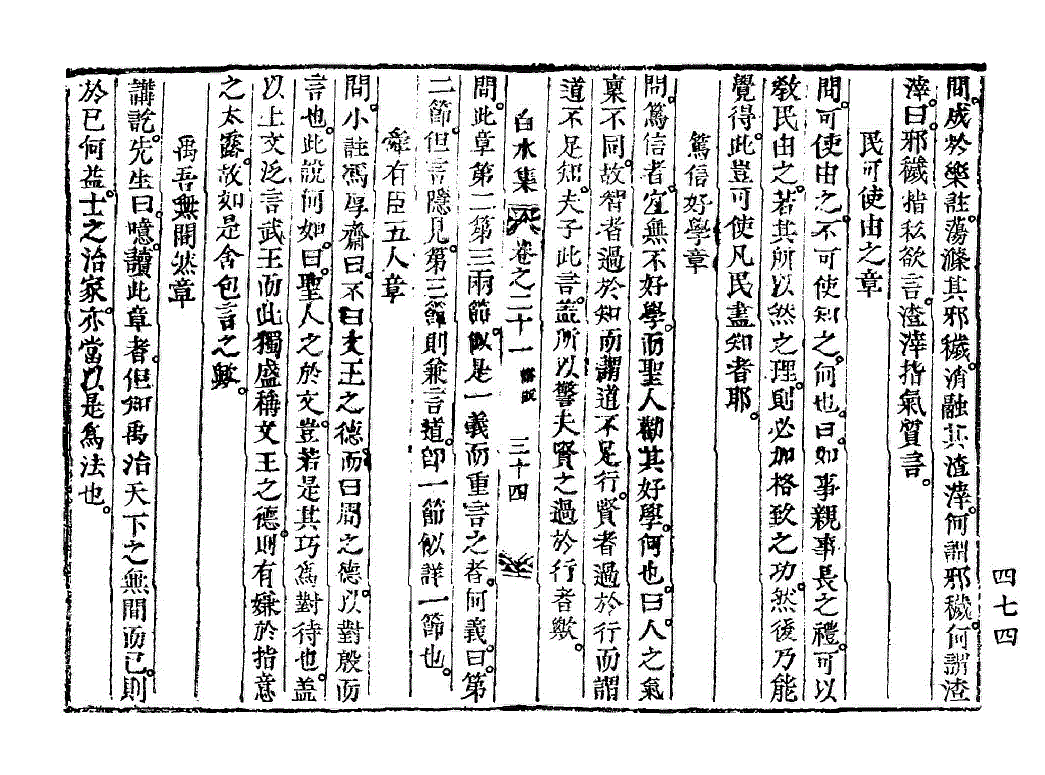 问。成于乐注。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何谓邪秽。何谓渣滓。曰。邪秽指私欲言。渣滓指气质言。
问。成于乐注。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何谓邪秽。何谓渣滓。曰。邪秽指私欲言。渣滓指气质言。民可使由之章
问。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也。曰。如事亲事长之礼。可以教民由之。若其所以然之理。则必加格致之功。然后乃能觉得。此岂可使凡民尽知者耶。
笃信好学章
问。笃信者。宜无不好学。而圣人劝其好学。何也。曰。人之气禀不同。故智者过于知而谓道不足行。贤者过于行而谓道不足知。夫子此言。盖所以警夫贤之过于行者欤。
问。此章第二第三两节。似是一义而重言之者。何义。曰。第二节。但言隐见。第三节则兼言道。即一节似详一节也。
舜有臣五人章
问。小注冯厚斋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对殷而言也。此说何如。曰。圣人之于文。岂若是其巧为对待也。盖以上文泛言武王而此独盛称文王之德。则有嫌于指意之太露。故如是含包言之欤。
禹吾无间然章
讲讫。先生曰。噫。读此章者。但知禹治天下之无间而已。则于己何益。士之治家。亦当以是为法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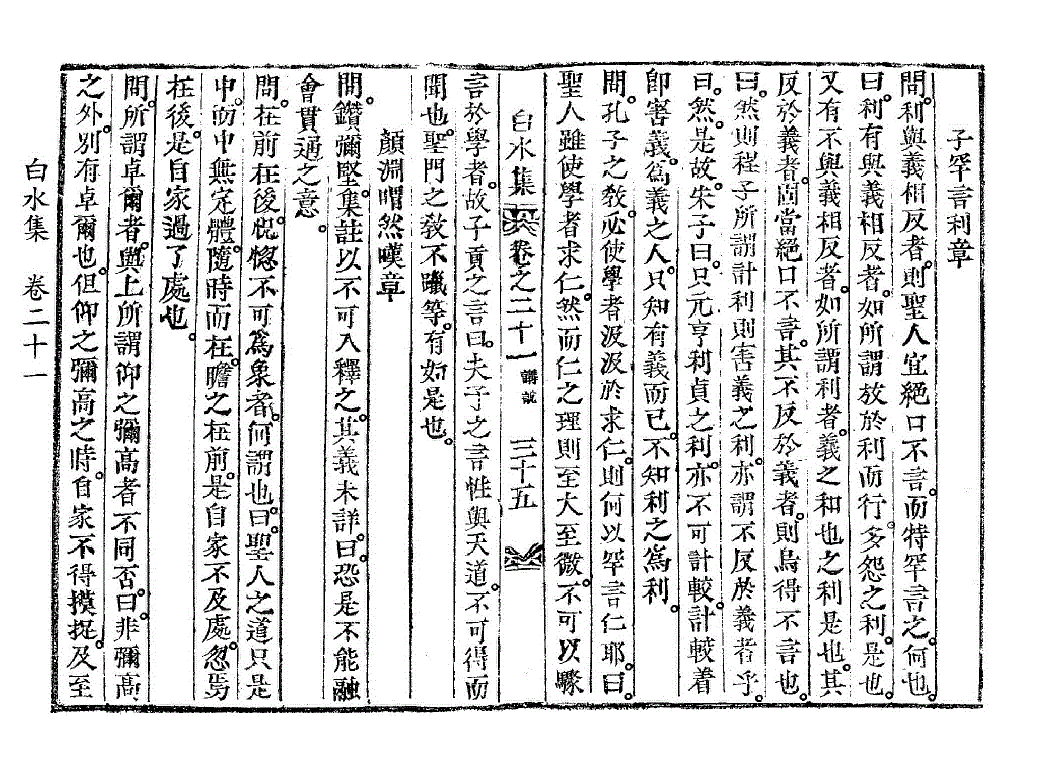 子罕言利章
子罕言利章问。利与义相反者。则圣人宜绝口不言。而特罕言之。何也。曰。利有与义相反者。如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之利。是也。又有不与义相反者。如所谓利者。义之和也之利是也。其反于义者。固当绝口不言。其不反于义者。则乌得不言也。曰。然则程子所谓计利则害义之利。亦谓不反于义者乎。曰。然。是故。朱子曰。只元亨利贞之利。亦不可计较。计较着即害义。为义之人。只知有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
问。孔子之教。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则何以罕言仁耶。曰。圣人虽使学者求仁。然而仁之理则至大至微。不可以骤言于学者。故子贡之言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圣门之教不躐等。有如是也。
颜渊喟然叹章
问。钻弥坚。集注以不可入释之。其义未详。曰。恐是不能融会贯通之意。
问。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者。何谓也。曰。圣人之道只是中。而中无定体。随时而在。瞻之在前。是自家不及处。忽焉在后。是自家过了处也。
问。所谓卓尔者。与上所谓仰之弥高者不同否。曰。非弥高之外。别有卓尔也。但仰之弥高之时。自家不得摸捉。及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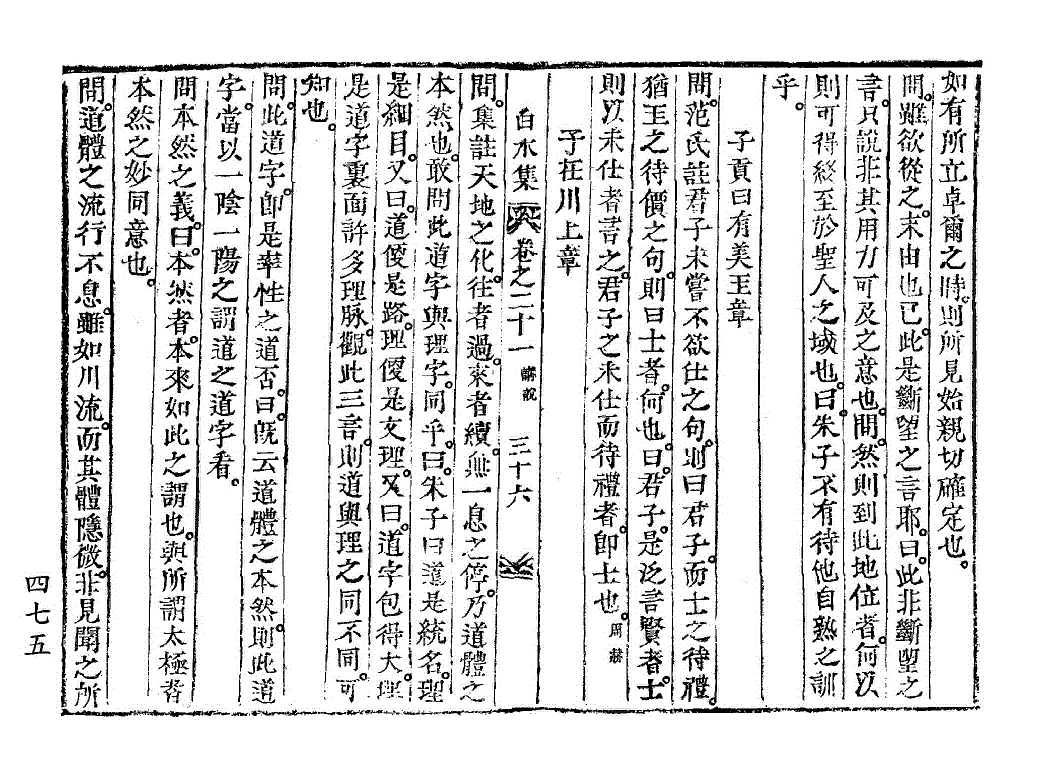 如有所立卓尔之时。则所见始亲切确定也。
如有所立卓尔之时。则所见始亲切确定也。问。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是断望之言耶。曰。此非断望之言。只说非其用力可及之意也。问。然则到此地位者。何以则可得终至于圣人之域也。曰。朱子不有待他自熟之训乎。
子贡曰有美玉章
问。范氏注君子未尝不欲仕之句。则曰君子。而士之待礼。犹玉之待价之句。则曰士者。何也。曰。君子。是泛言贤者。士则以未仕者言之。君子之未仕而待礼者。即士也。(周赫)
子在川上章
问。集注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敢问此道字与理字。同乎。曰。朱子曰道是统名。理是细目。又曰。道便是路。理便是文理。又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观此三言。则道与理之同不同。可知也。
问。此道字。即是率性之道否。曰。既云道体之本然。则此道字。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之道字看。
问本然之义。曰。本然者。本来如此之谓也。与所谓太极者。本然之妙同意也。
问。道体之流行不息。虽如川流。而其体隐微。非见闻之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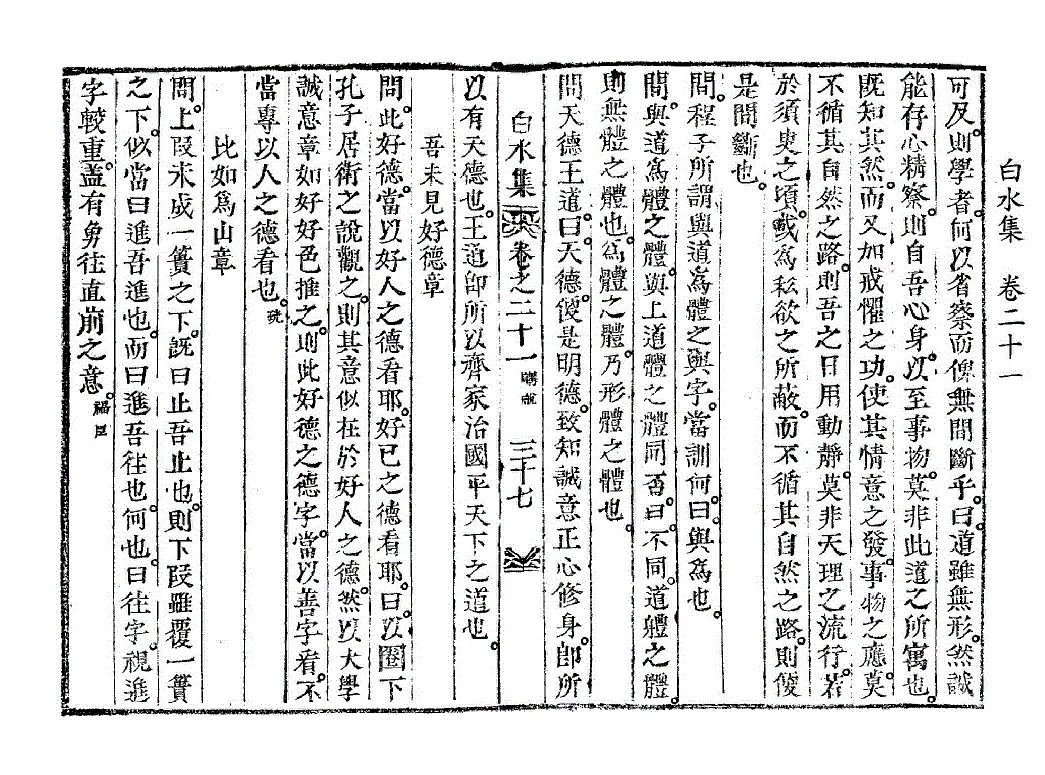 可及。则学者。何以省察而俾无间断乎。曰。道虽无形。然诚能存心精察。则自吾心身。以至事物。莫非此道之所寓也。既知其然。而又加戒惧之功。使其情意之发。事物之应。莫不循其自然之路。则吾之日用动静。莫非天理之流行。若于须臾之顷。或为私欲之所蔽。而不循其自然之路。则便是间断也。
可及。则学者。何以省察而俾无间断乎。曰。道虽无形。然诚能存心精察。则自吾心身。以至事物。莫非此道之所寓也。既知其然。而又加戒惧之功。使其情意之发。事物之应。莫不循其自然之路。则吾之日用动静。莫非天理之流行。若于须臾之顷。或为私欲之所蔽。而不循其自然之路。则便是间断也。问。程子所谓与道为体之与字。当训何。曰。与为也。
问。与道为体之体。与上道体之体同否。曰。不同。道体之体。则无体之体也。为体之体。乃形体之体也。
问天德王道。曰。天德。便是明德。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所以有天德也。王道即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也。
吾未见好德章
问。此好德。当以好人之德看耶。好己之德看耶。曰。以圈下孔子居卫之说观之。则其意似在于好人之德。然以大学诚意章如好好色推之。则此好德之德字。当以善字看。不当专以人之德看也。(珖)
比如为山章
问。上段未成一篑之下。既曰止吾止也。则下段虽覆一篑之下。似当曰进吾进也。而曰进吾往也。何也。曰往字。视进字较重。盖有勇往直前之意。(福臣)
衣弊缊袍章
问。衣缊袍不耻者。此闻道之功效邪。曰。志道之士。固当不耻恶衣食。然孔门弟子之闻道者。亦多矣。独于子路而称之。此非但闻道之效。抑其气质有卓然者欤。(宗甲)
可与共学章
问。程子注。与杨氏注。不同邪。何有圈内外之分也。曰。程子注则从大文文势而顺释之。杨氏注则反大文文势而逆释之。所以有圈内外之分也。(周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外集 第 4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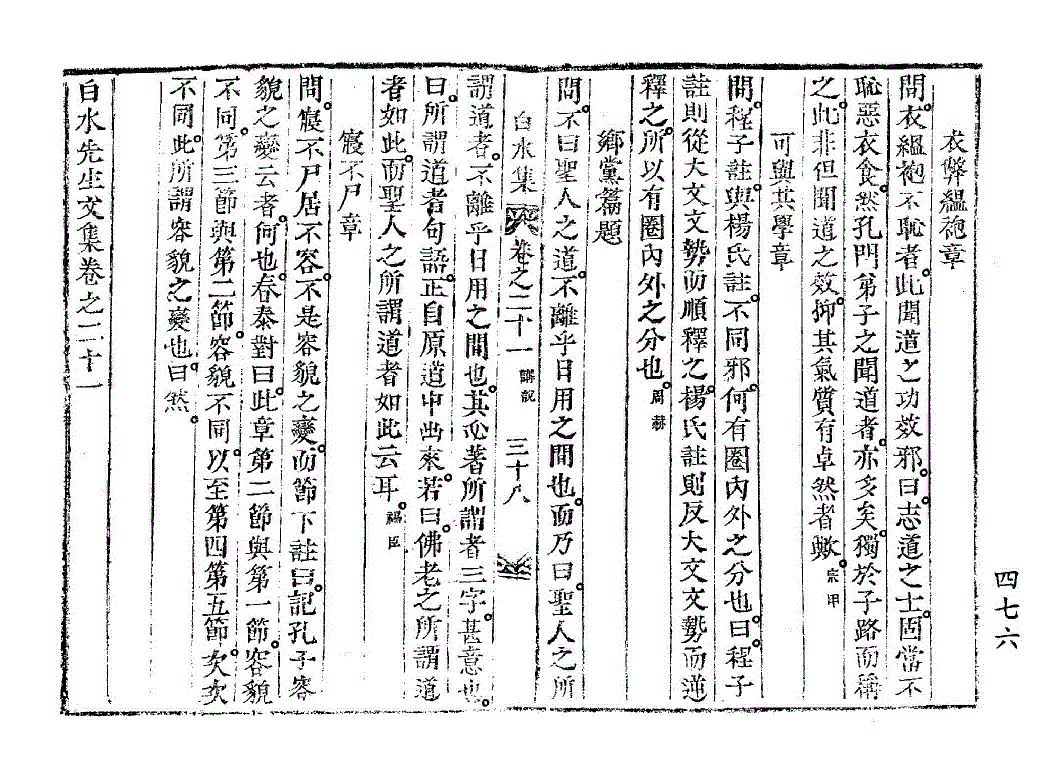 乡党篇题
乡党篇题问。不曰圣人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也。而乃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其必著所谓者三字。甚意也。曰。所谓道者句语。正自原道中出来。若曰。佛老之所谓道者如此。而圣人之所谓道者如此云耳。(福臣)
寝不尸章
问。寝不尸居不容。不是容貌之变。而节下注曰。记孔子容貌之变云者。何也。春泰对曰。此章第二节与第一节。容貌不同。第三节与第二节。容貌不同。以至第四第五节。次次不同。此所谓容貌之变也。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