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大学讲说
大学讲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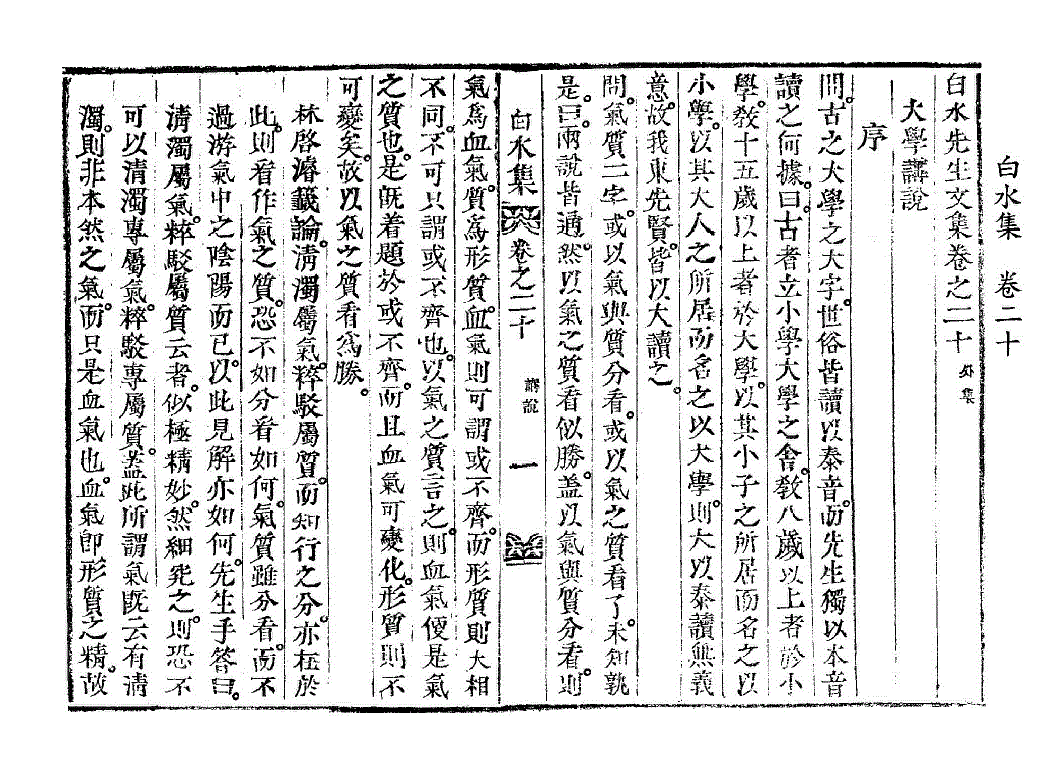 序
序问。古之大学之大字。世俗皆读以泰音。而先生独以本音读之何据。曰。古者立小学大学之舍。教八岁以上者于小学。教十五岁以上者于大学。以其小子之所居而名之以小学。以其大人之所居而名之以大学。则大以泰读无义意。故我东先贤。皆以大读之。
问。气质二字。或以气与质分看。或以气之质看了。未知孰是。曰。两说皆通。然以气之质看似胜。盖以气与质分看。则气为血气。质为形质。血气则可谓或不齐。而形质则大相不同。不可只谓或不齐也。以气之质言之。则血气便是气之质也。是既着题于或不齐。而且血气可变化。形质则不可变矣。故以气之质看为胜。
林启浚签论。清浊属气。粹驳属质。而知行之分。亦在于此。则看作气之质。恐不如分看如何。气质虽分看。而不过游气中之阴阳而已。以此见解亦如何。先生手答曰。清浊属气。粹驳属质云者。似极精妙。然细究之。则恐不可以清浊专属气。粹驳专属质。盖此所谓气既云有清浊。则非本然之气。而只是血气也。血气即形质之精。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4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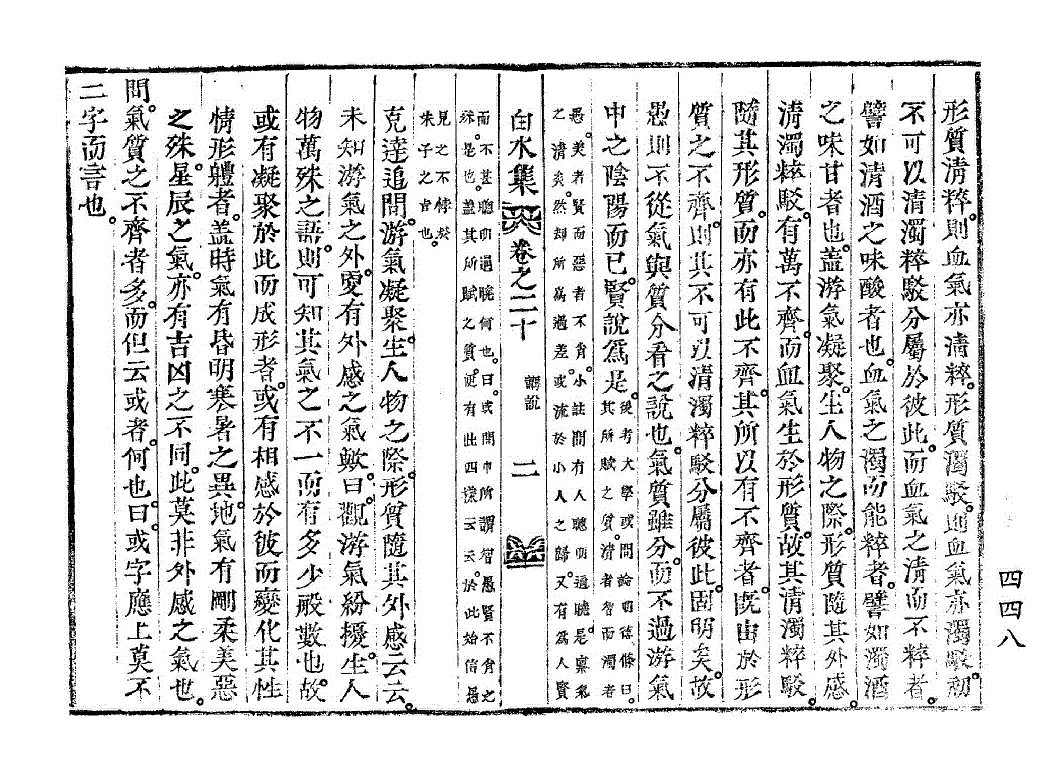 形质清粹。则血气亦清粹。形质浊驳。则血气亦浊驳。初不可以清浊粹驳分属于彼此。而血气之清而不粹者。譬如清酒之味酸者也。血气之浊而能粹者。譬如浊酒之味甘者也。盖游气凝聚。生人物之际。形质随其外感。清浊粹驳。有万不齐。而血气生于形质。故其清浊粹驳。随其形质。而亦有此不齐。其所以有不齐者。既由于形质之不齐。则其不可以清浊粹驳分属彼此。固明矣。故愚则不从气与质分看之说也。气质虽分。而不过游气中之阴阳而已。贤说为是。(后考大学或问论明德条曰。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小注问有人聪明通晓。是禀气之清矣。然却所为过差。或流于小人之归。又有为人贤不甚聪明通晓何也。曰。或问中所谓智愚贤不肖之殊。是也。盖其所赋之质。便有此四样云云。于此始信愚见之不悖于朱子之旨也。)
形质清粹。则血气亦清粹。形质浊驳。则血气亦浊驳。初不可以清浊粹驳分属于彼此。而血气之清而不粹者。譬如清酒之味酸者也。血气之浊而能粹者。譬如浊酒之味甘者也。盖游气凝聚。生人物之际。形质随其外感。清浊粹驳。有万不齐。而血气生于形质。故其清浊粹驳。随其形质。而亦有此不齐。其所以有不齐者。既由于形质之不齐。则其不可以清浊粹驳分属彼此。固明矣。故愚则不从气与质分看之说也。气质虽分。而不过游气中之阴阳而已。贤说为是。(后考大学或问论明德条曰。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小注问有人聪明通晓。是禀气之清矣。然却所为过差。或流于小人之归。又有为人贤不甚聪明通晓何也。曰。或问中所谓智愚贤不肖之殊。是也。盖其所赋之质。便有此四样云云。于此始信愚见之不悖于朱子之旨也。)克达追问。游气凝聚。生人物之际。形质随其外感云云。未知游气之外。更有外感之气欤。曰。观游气纷扰。生人物万殊之语。则可知其气之不一而有多少般数也。故或有凝聚于此而成形者。或有相感于彼而变化其性情形体者。盖时气有昏明寒暑之异。地气有刚柔美恶之殊。星辰之气。亦有吉凶之不同。此莫非外感之气也。
问。气质之不齐者多。而但云或者。何也。曰。或字应上莫不二字而言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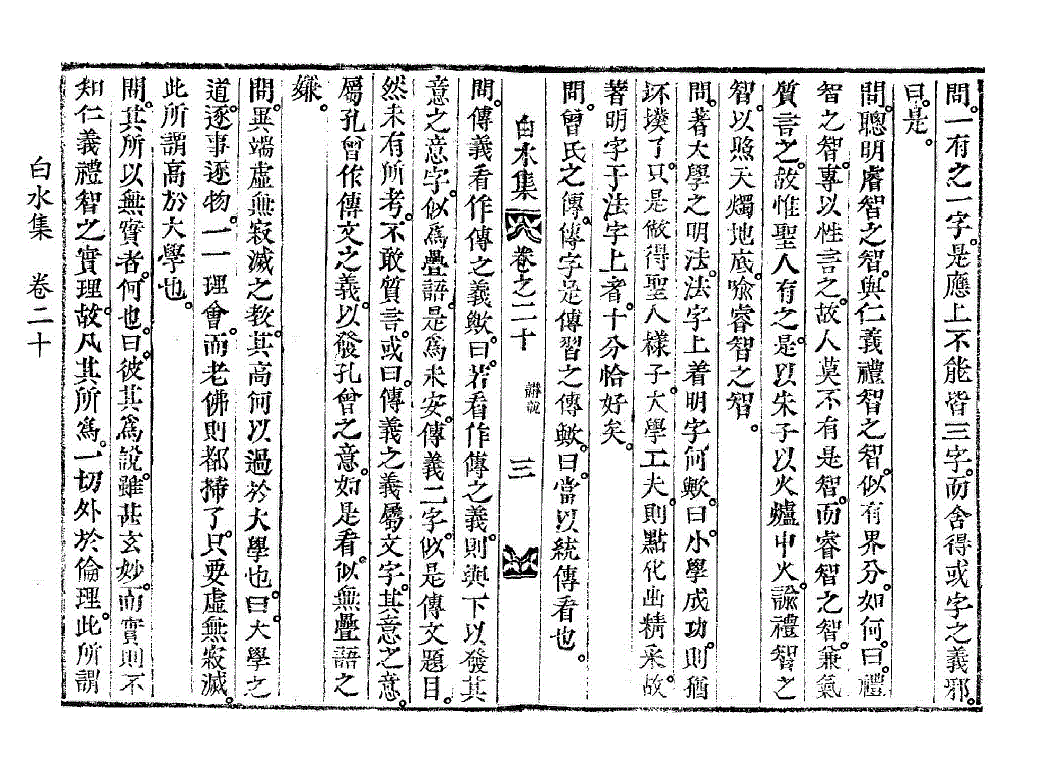 问。一有之一字。是应上不能皆三字。而含得或字之义邪。曰。是。
问。一有之一字。是应上不能皆三字。而含得或字之义邪。曰。是。问。聪明睿智之智。与仁义礼智之智。似有界分。如何。曰。礼智之智。专以性言之。故人莫不有是智。而睿智之智。兼气质言之。故惟圣人有之。是以朱子以火炉中火。谕礼智之智。以照天烛地底。喻睿智之智。
问。著大学之明法。法字上着明字何欤。曰。小学成功。则犹坏墣了。只是做得圣人样子。大学工夫。则点化出精采。故著明字于法字上者。十分恰好矣。
问。曾氏之传。传字是传习之传欤。曰。当以统传看也。
问。传义看作传之义欤。曰。若看作传之义。则与下以发其意之意字。似为叠语。是为未安。传义二字。似是传文题目。然未有所考。不敢质言。或曰。传义之义属文字。其意之意。属孔曾作传文之义。以发孔曾之意。如是看。似无叠语之嫌。
问。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何以过于大学也。曰。大学之道。逐事逐物。一一理会。而老佛则都扫了。只要虚无寂灭。此所谓高于大学也。
问。其所以无实者。何也。曰。彼其为说。虽甚玄妙。而实则不知仁义礼智之实理。故凡其所为。一切外于伦理。此所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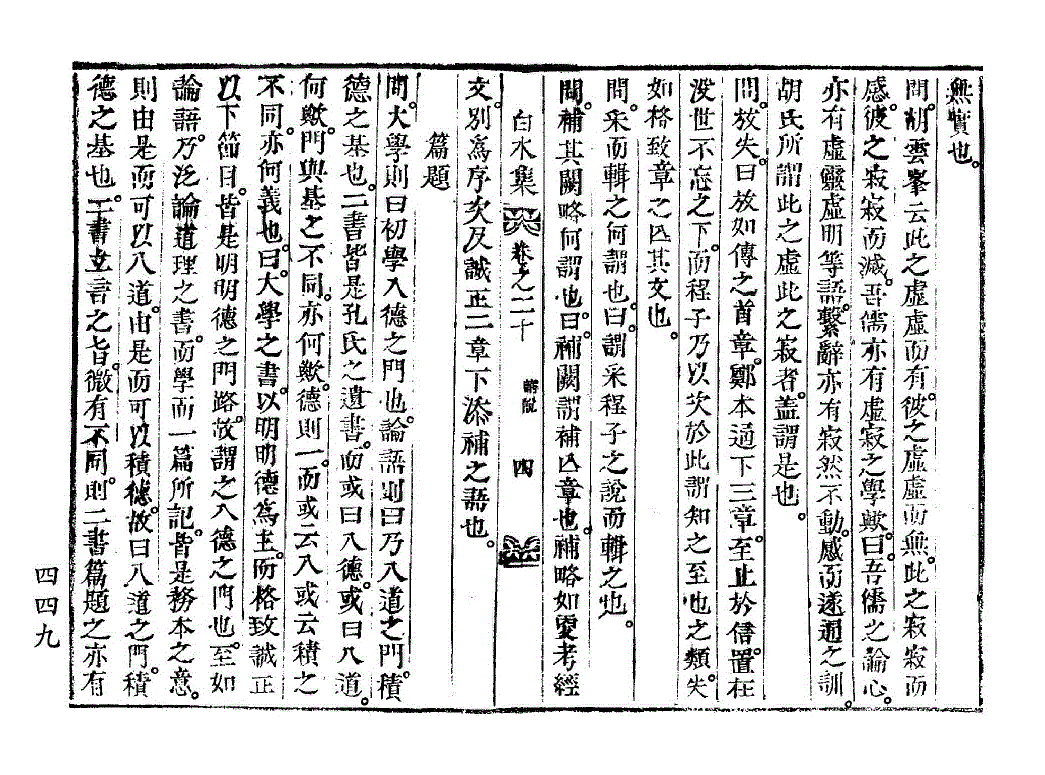 无实也。
无实也。问。胡云峰云此之虚虚而有。彼之虚虚而无。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灭。吾儒亦有虚寂之学欤。曰。吾儒之论心。亦有虚灵虚明等语。系辞亦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训。胡氏所谓此之虚此之寂者。盖谓是也。
问。放失。曰放如传之首章。郑本通下三章。至止于信。置在没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于此谓知之至也之类。失如格致章之亡其文也。
问。采而辑之何谓也。曰。谓采程子之说而辑之也。
问。补其阙略何谓也。曰。补阙谓补亡章也。补略如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及诚正二章下添补之语也。
篇题
问。大学则曰初学入德之门也。论语则曰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也。二书皆是孔氏之遗书。而或曰入德。或曰入道。何欤。门与基之不同。亦何欤。德则一。而或云入或云积之不同。亦何义也。曰。大学之书。以明明德为主。而格致诚正以下节目。皆是明明德之门路。故谓之入德之门也。至如论语。乃泛论道理之书。而学而一篇所记。皆是务本之意。则由是而可以入道。由是而可以积德。故曰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也。二书立言之旨。微有不同。则二书篇题之亦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0H 页
 不同。何足疑哉。门以所从入而名之也。基以所积累而言之也。德则一而或云入或云积者。盖德有二义。有得于天而为人本心者。明德。是也。有行道而有得于心者。如据于德。是也。故于得于天之德。则可以入言。而不可以积言之也。于行道而得于心之德。则可以积言。而不可以入言之也。
不同。何足疑哉。门以所从入而名之也。基以所积累而言之也。德则一而或云入或云积者。盖德有二义。有得于天而为人本心者。明德。是也。有行道而有得于心者。如据于德。是也。故于得于天之德。则可以入言。而不可以积言之也。于行道而得于心之德。则可以积言。而不可以入言之也。经一章
问。明德或以为性。或以为心。何说为是。曰。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小注又云虚灵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无少欠阙。便是性。随感而动。便是情。观此可以知明德之为心统性情者也。
问。以此章句及小注说观之则然矣。然传之首章顾諟天之明命。章句曰。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小注曰。天之所以与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为性者。便是明德。此非以明德为性者乎。曰。此固为以明德为性者之證案。然若因此小注。而遂以明德为性。则与明德章句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之说相左。今若以性为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则不成道理也。
问。明德果是心。则经文不曰明心。而必曰明明德何也。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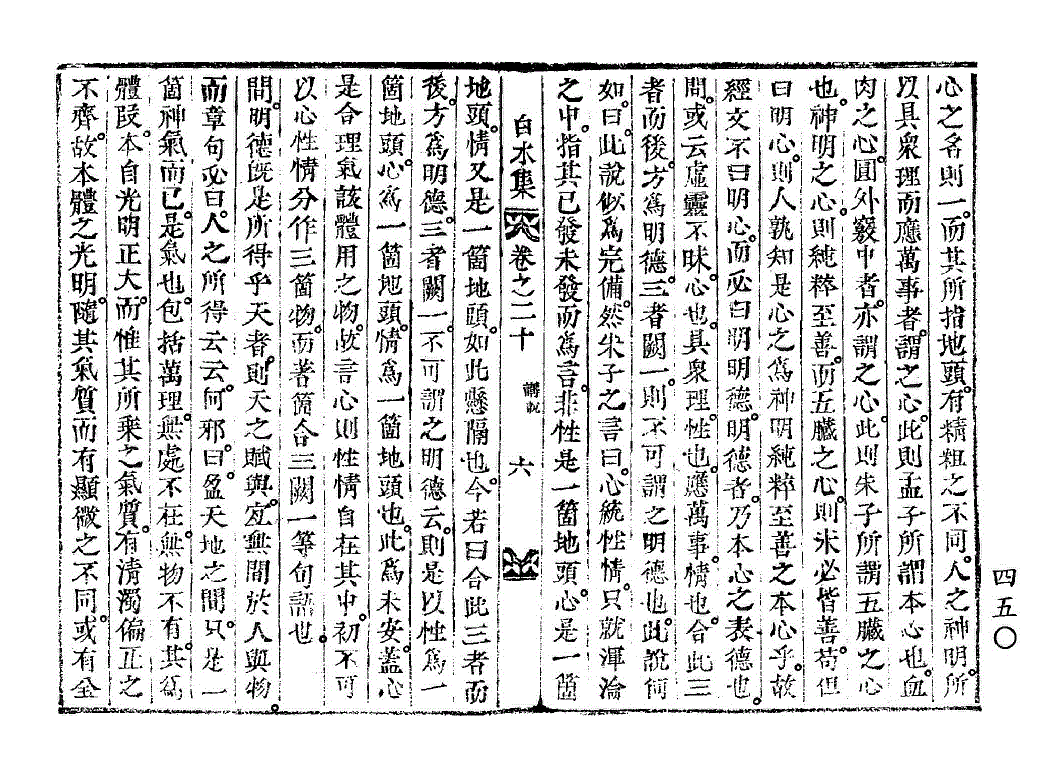 心之名则一。而其所指地头。有精粗之不同。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谓之心。此则孟子所谓本心也。血肉之心。圆外窍中者。亦谓之心。此则朱子所谓五脏之心也。神明之心。则纯粹至善。而五脏之心。则未必皆善。苟但曰明心。则人孰知是心之为神明纯粹至善之本心乎。故经文不曰明心。而必曰明明德。明德者。乃本心之表德也。
心之名则一。而其所指地头。有精粗之不同。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谓之心。此则孟子所谓本心也。血肉之心。圆外窍中者。亦谓之心。此则朱子所谓五脏之心也。神明之心。则纯粹至善。而五脏之心。则未必皆善。苟但曰明心。则人孰知是心之为神明纯粹至善之本心乎。故经文不曰明心。而必曰明明德。明德者。乃本心之表德也。问。或云虚灵不昧。心也。具众理。性也。应万事。情也。合此三者而后。方为明德。三者阙一。则不可谓之明德也。此说何如。曰。此说似为完备。然朱子之言曰。心统性情。只就浑沦之中。指其已发未发而为言。非性是一个地头。心是一个地头。情又是一个地头。如此悬隔也。今若曰合此三者而后。方为明德。三者阙一。不可谓之明德云。则是以性为一个地头。心为一个地头。情为一个地头也。此为未安。盖心是合理气该体用之物。故言心则性情自在其中。初不可以心性情分作三个物。而著个合三阙一等句语也。
问。明德既是所得乎天者。则天之赋与。宜无间于人与物。而章句必曰。人之所得云云。何邪。曰。盈天地之间。只是一个神气而已。是气也。包括万理。无处不在。无物不有。其为体段。本自光明正大。而惟其所乘之气质。有清浊偏正之不齐。故本体之光明。随其气质而有显微之不同。或有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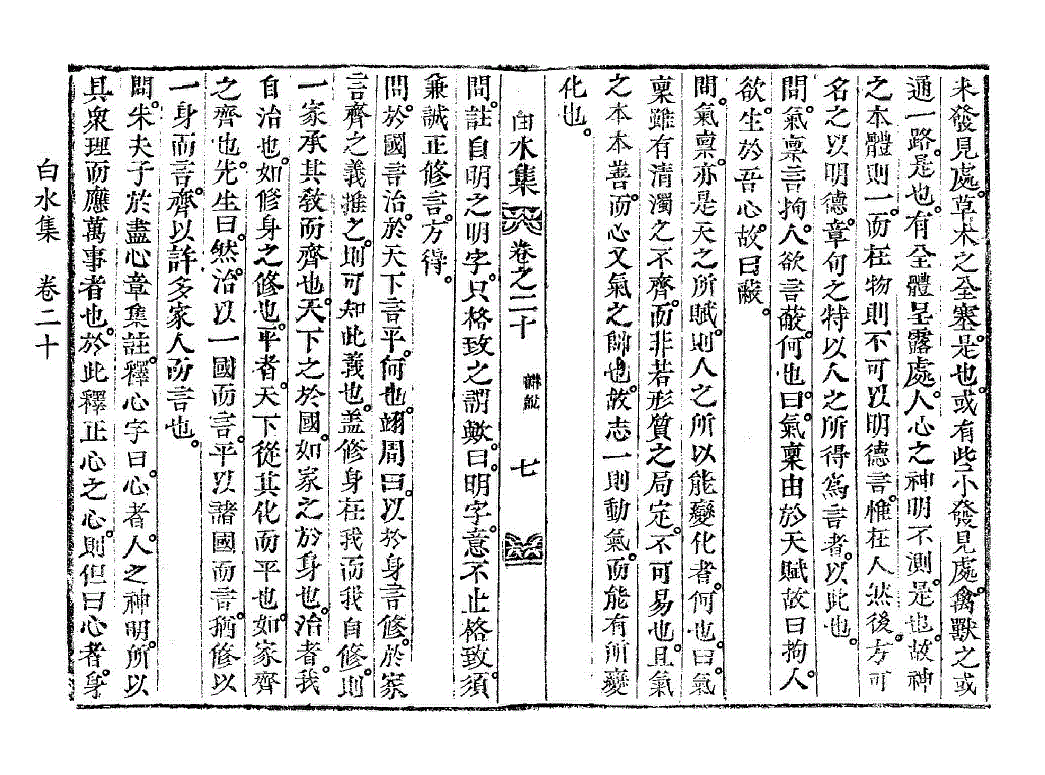 未发见处。草木之全塞。是也。或有些小发见处。禽兽之或通一路。是也。有全体呈露处。人心之神明不测。是也。故神之本体则一。而在物则不可以明德言。惟在人然后。方可名之以明德。章句之特以人之所得为言者。以此也。
未发见处。草木之全塞。是也。或有些小发见处。禽兽之或通一路。是也。有全体呈露处。人心之神明不测。是也。故神之本体则一。而在物则不可以明德言。惟在人然后。方可名之以明德。章句之特以人之所得为言者。以此也。问。气禀言拘。人欲言蔽。何也。曰。气禀由于天赋故曰拘。人欲。生于吾心。故曰蔽。
问。气禀。亦是天之所赋。则人之所以能变化者。何也。曰。气禀虽有清浊之不齐。而非若形质之局定。不可易也。且气之本本善。而心又气之帅也。故志一则动气。而能有所变化也。
问。注自明之明字。只格致之谓欤。曰。明字。意不止格致。须兼诚正修言。方得。
问。于国言治。于天下言平。何也。翊周曰。以于身言修。于家言齐之义推之。则可知此义也。盖修身在我而我自修。则一家承其教而齐也。天下之于国。如家之于身也。治者。我自治也。如修身之修也。平者。天下从其化而平也。如家齐之齐也。先生曰。然。治以一国而言。平以诸国而言。犹修以一身而言。齐以许多家人而言也。
问。朱夫子于尽心章集注。释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于此释正心之心。则但曰心者。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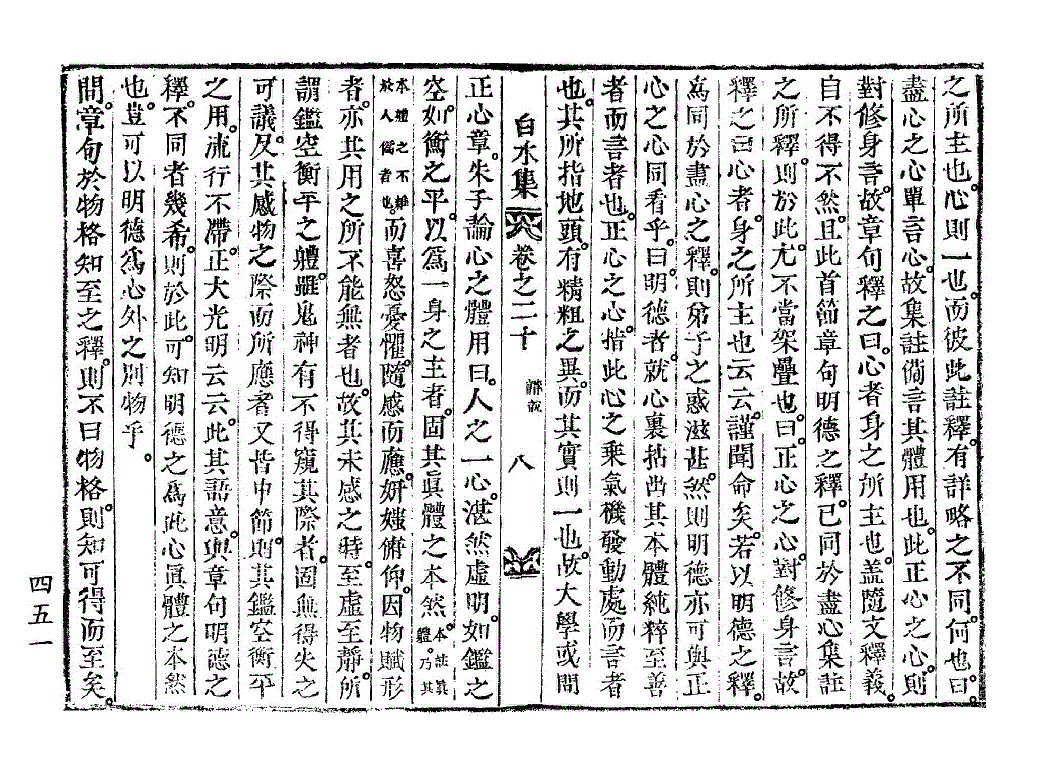 之所主也。心则一也。而彼此注释。有详略之不同。何也。曰。尽心之心单言心。故集注备言其体用也。此正心之心。则对修身言。故章句释之曰。心者身之所主也。盖随文释义。自不得不然。且此首节章句明德之释。已同于尽心集注之所释。则于此。尤不当架叠也。曰。正心之心。对修身言。故释之曰心者。身之所主也云云。谨闻命矣。若以明德之释。为同于尽心之释。则弟子之惑滋甚。然则明德亦可与正心之心同看乎。曰。明德者。就心里拈出其本体纯粹至善者而言者也。正心之心。指此心之乘气机发动处而言者也。其所指地头。有精粗之异。而其实则一也。故大学或问正心章。朱子论心之体用曰。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本注真体。乃其本体之不杂于人伪者也。)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故其未感之时。至虚至静。所谓鉴空衡平之体。虽鬼神有不得窥其际者。固无得失之可议。及其感物之际而所应者又皆中节。则其鉴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滞。正大光明云云。此其语意。与章句明德之释。不同者几希。则于此。可知明德之为此心真体之本然也。岂可以明德为心外之别物乎。
之所主也。心则一也。而彼此注释。有详略之不同。何也。曰。尽心之心单言心。故集注备言其体用也。此正心之心。则对修身言。故章句释之曰。心者身之所主也。盖随文释义。自不得不然。且此首节章句明德之释。已同于尽心集注之所释。则于此。尤不当架叠也。曰。正心之心。对修身言。故释之曰心者。身之所主也云云。谨闻命矣。若以明德之释。为同于尽心之释。则弟子之惑滋甚。然则明德亦可与正心之心同看乎。曰。明德者。就心里拈出其本体纯粹至善者而言者也。正心之心。指此心之乘气机发动处而言者也。其所指地头。有精粗之异。而其实则一也。故大学或问正心章。朱子论心之体用曰。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本注真体。乃其本体之不杂于人伪者也。)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故其未感之时。至虚至静。所谓鉴空衡平之体。虽鬼神有不得窥其际者。固无得失之可议。及其感物之际而所应者又皆中节。则其鉴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滞。正大光明云云。此其语意。与章句明德之释。不同者几希。则于此。可知明德之为此心真体之本然也。岂可以明德为心外之别物乎。问。章句于物格知至之释。则不曰物格。则知可得而至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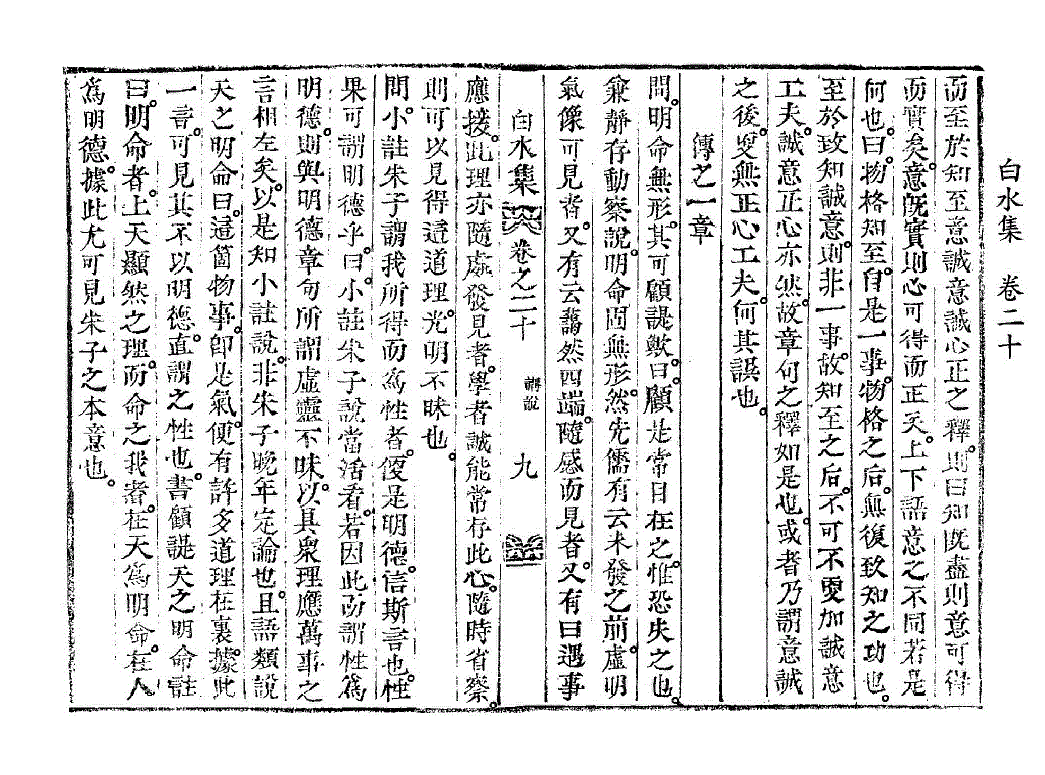 而至于知至意诚意诚心正之释。则曰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上下语意之不同若是何也。曰。物格知至。自是一事。物格之后。无复致知之功也。至于致知诚意。则非一事。故知至之后。不可不更加诚意工夫。诚意正心亦然。故章句之释如是也。或者乃谓意诚之后。更无正心工夫。何其误也。
而至于知至意诚意诚心正之释。则曰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上下语意之不同若是何也。曰。物格知至。自是一事。物格之后。无复致知之功也。至于致知诚意。则非一事。故知至之后。不可不更加诚意工夫。诚意正心亦然。故章句之释如是也。或者乃谓意诚之后。更无正心工夫。何其误也。传之一章
问。明命无形。其可顾諟欤。曰。顾是常目在之。惟恐失之也。兼静存动察说。明命固无形。然先儒有云未发之前。虚明气像可见者。又有云蔼然四端。随感而见者。又有曰遇事应接。此理亦随处发见者。学者诚能常存此心。随时省察。则可以见得这道理。光明不昧也。
问。小注朱子谓我所得而为性者。便是明德。信斯言也。性果可谓明德乎。曰。小注朱子说当活看。若因此而谓性为明德。则与明德章句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之言相左矣。以是知小注说。非朱子晚年定论也。且语类说天之明命曰。这个物事。即是气。便有许多道理在里。据此一言。可见其不以明德。直谓之性也。书顾諟天之明命注曰。明命者。上天显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为明命。在人为明德。据此尤可见朱子之本意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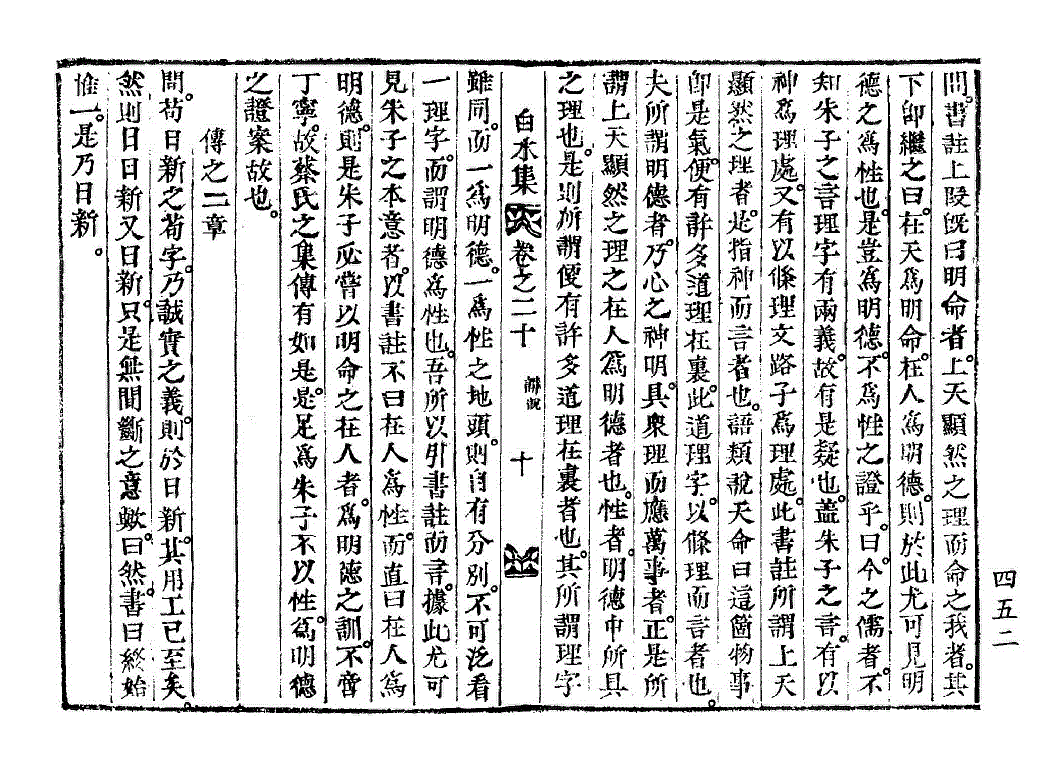 问。书注上段既曰明命者。上天显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其下即继之曰。在天为明命。在人为明德。则于此尤可见明德之为性也。是岂为明德。不为性之證乎。曰。今之儒者。不知朱子之言理字有两义。故有是疑也。盖朱子之言。有以神为理处。又有以条理文路子为理处。此书注所谓上天显然之理者。是指神而言者也。语类说天命曰这个物事即是气。便有许多道理在里。此道理字。以条理而言者也。夫所谓明德者。乃心之神明。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正是所谓上天显然之理之在人为明德者也。性者。明德中所具之理也。是则所谓便有许多道理在里者也。其所谓理字虽同。而一为明德。一为性之地头。则自有分别。不可泛看一理字。而谓明德为性也。吾所以引书注而言。据此尤可见朱子之本意者。以书注不曰在人为性。而直曰在人为明德。则是朱子必尝以明命之在人者。为明德之训。不啻丁宁。故蔡氏之集传有如是。是足为朱子不以性。为明德之證案故也。
问。书注上段既曰明命者。上天显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其下即继之曰。在天为明命。在人为明德。则于此尤可见明德之为性也。是岂为明德。不为性之證乎。曰。今之儒者。不知朱子之言理字有两义。故有是疑也。盖朱子之言。有以神为理处。又有以条理文路子为理处。此书注所谓上天显然之理者。是指神而言者也。语类说天命曰这个物事即是气。便有许多道理在里。此道理字。以条理而言者也。夫所谓明德者。乃心之神明。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正是所谓上天显然之理之在人为明德者也。性者。明德中所具之理也。是则所谓便有许多道理在里者也。其所谓理字虽同。而一为明德。一为性之地头。则自有分别。不可泛看一理字。而谓明德为性也。吾所以引书注而言。据此尤可见朱子之本意者。以书注不曰在人为性。而直曰在人为明德。则是朱子必尝以明命之在人者。为明德之训。不啻丁宁。故蔡氏之集传有如是。是足为朱子不以性。为明德之證案故也。传之二章
问。苟日新之苟字。乃诚实之义。则于日新。其用工已至矣。然则日日新又日新。只是无间断之意欤。曰然。书曰终始惟一。是乃日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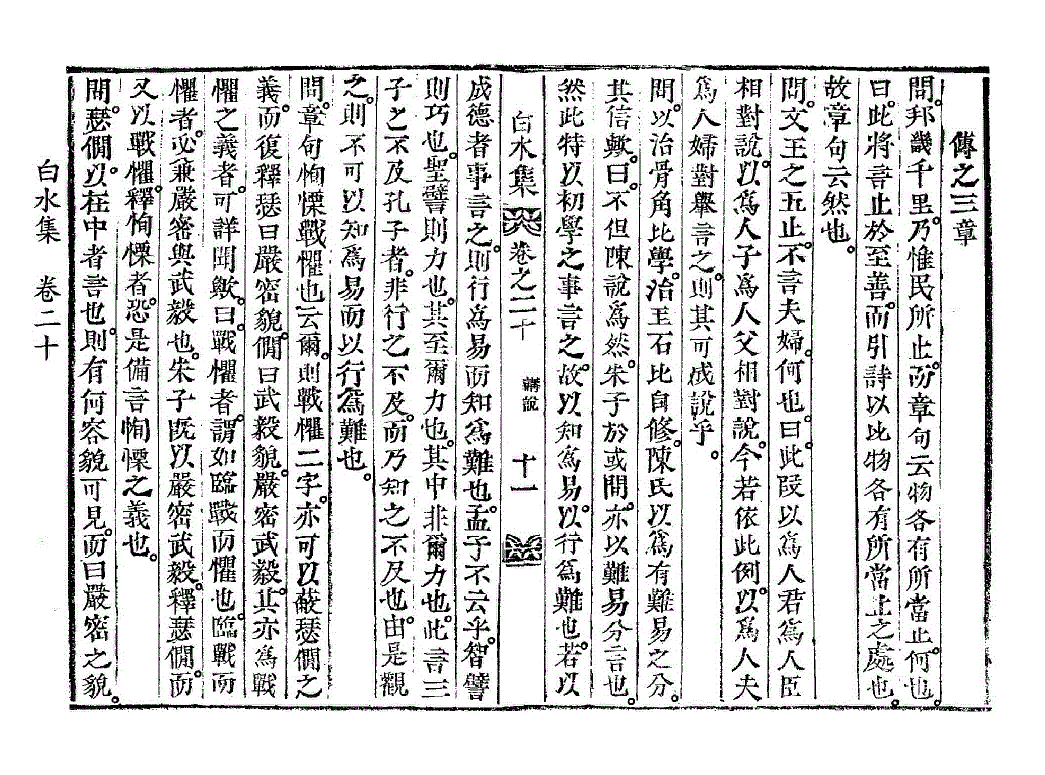 传之三章
传之三章问。邦畿千里。乃惟民所止。而章句云物各有所当止。何也。曰。此将言止于至善。而引诗以比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故章句云然也。
问。文王之五止。不言夫妇。何也。曰。此段以为人君为人臣相对说。以为人子为人父相对说。今若依此例。以为人夫为人妇对举言之。则其可成说乎。
问。以治骨角比学。治玉石比自修。陈氏以为有难易之分。其信欤。曰。不但陈说为然。朱子于或问。亦以难易分言也。然此特以初学之事言之。故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若以成德者事言之。则行为易而知为难也。孟子不云乎。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此言三子之不及孔子者。非行之不及。而乃知之不及也。由是观之。则不可以知为易而以行为难也。
问。章句恂慄战惧也云尔。则战惧二字。亦可以蔽瑟僩之义。而复释瑟曰严密貌。僩曰武毅貌。严密武毅。其亦为战惧之义者。可详闻欤。曰。战惧者。谓如临战而惧也。临战而惧者。必兼严密与武毅也。朱子既以严密武毅。释瑟僩。而又以战惧。释恂慄者。恐是备言恂慄之义也。
问。瑟僩。以在中者言也。则有何容貌可见。而曰严密之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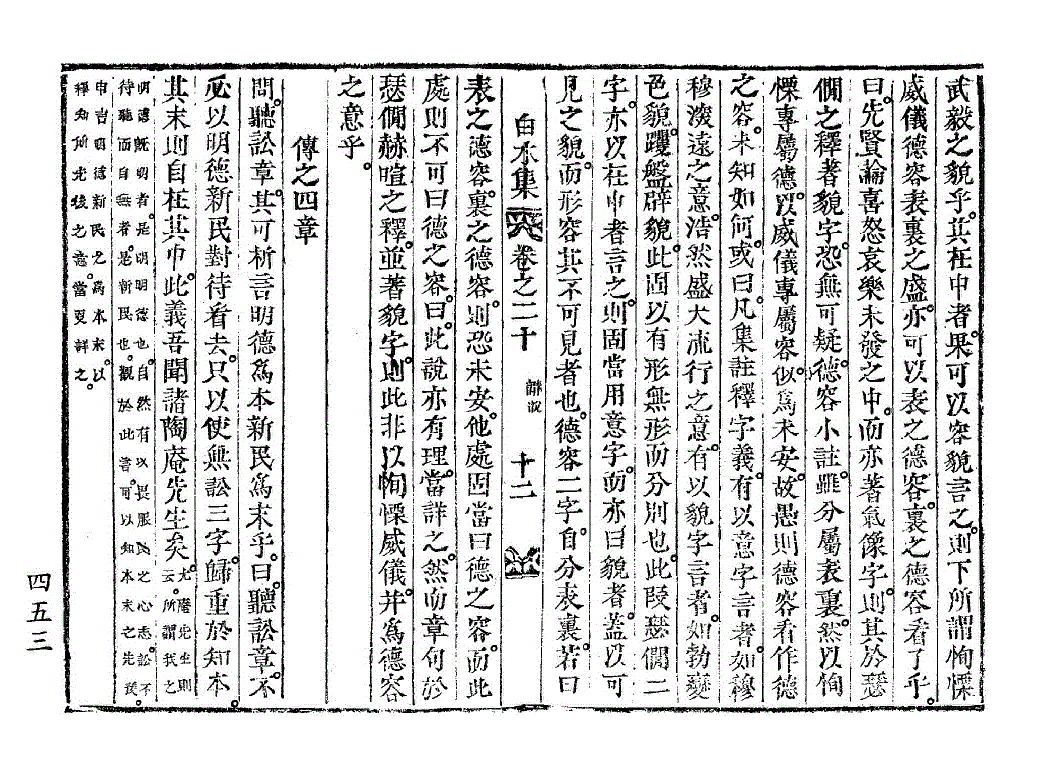 武毅之貌乎。其在中者。果可以容貌言之。则下所谓恂慄威仪德容表里之盛。亦可以表之德容。里之德容看了乎。曰。先贤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亦著气像字。则其于瑟僩之释著貌字。恐无可疑。德容小注。虽分属表里。然以恂慄专属德。以威仪专属容。似为未安。故愚则德容看作德之容。未知如何。或曰。凡集注释字义。有以意字言者。如穆穆深远之意。浩然盛大流行之意。有以貌字言者。如勃变色貌。躩盘辟貌。此固以有形无形而分别也。此段瑟僩二字。亦以在中者言之。则固当用意字。而亦曰貌者。盖以可见之貌。而形容其不可见者也。德容二字。自分表里。若曰表之德容。里之德容。则恐未安。他处固当曰德之容。而此处则不可曰德之容。曰。此说亦有理。当详之。然而章句于瑟僩赫喧之释。并著貌字。则此非以恂慄威仪。并为德容之意乎。
武毅之貌乎。其在中者。果可以容貌言之。则下所谓恂慄威仪德容表里之盛。亦可以表之德容。里之德容看了乎。曰。先贤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亦著气像字。则其于瑟僩之释著貌字。恐无可疑。德容小注。虽分属表里。然以恂慄专属德。以威仪专属容。似为未安。故愚则德容看作德之容。未知如何。或曰。凡集注释字义。有以意字言者。如穆穆深远之意。浩然盛大流行之意。有以貌字言者。如勃变色貌。躩盘辟貌。此固以有形无形而分别也。此段瑟僩二字。亦以在中者言之。则固当用意字。而亦曰貌者。盖以可见之貌。而形容其不可见者也。德容二字。自分表里。若曰表之德容。里之德容。则恐未安。他处固当曰德之容。而此处则不可曰德之容。曰。此说亦有理。当详之。然而章句于瑟僩赫喧之释。并著貌字。则此非以恂慄威仪。并为德容之意乎。传之四章
问。听讼章。其可析言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乎。曰。听讼章。不必以明德新民对待看去。只以使无讼三字。归重于知本。其末则自在其中。此义吾闻诸陶庵先生矣。(尤庵先生则云。所谓我之明德既明者。是明明德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讼不待听而自无者。是新民也。观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后。申言明德新民之为本末。以释知所先后之意。当更详之。)
传之五章
问。莫不有知。其知有不尽。因其已知之理。三个知字同欤。曰。尤庵以莫不因其已知之知。谓不同于有知之知。而我陶庵先生。则以三知字。谓一串贯来。未知孰是。读者当致思自得焉。
问。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是谓众物之表之理里之理精之理粗之理。无不到乎。若尔则理亦有表里精粗之殊乎。曰先儒谓表是理之大纲。里是理之节目。精是理之细微。粗是理之浅近。无不到。是格得详尽。请更思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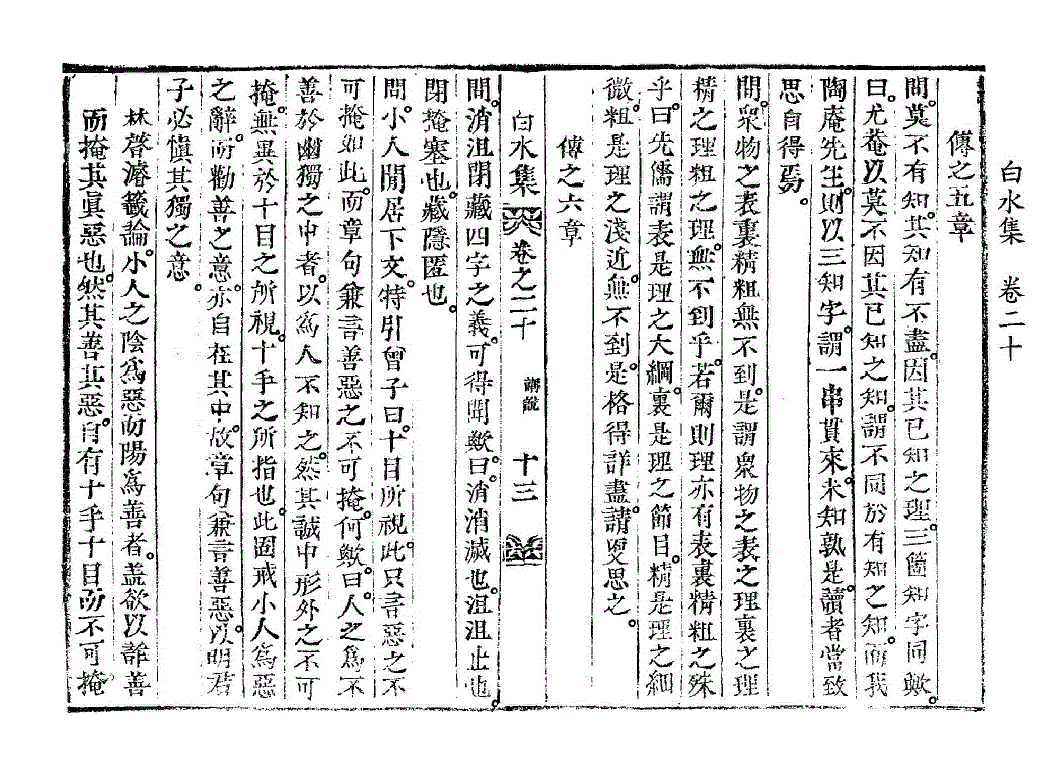 传之六章
传之六章问。消沮闭藏四字之义。可得闻欤。曰。消消灭也。沮沮止也。闭掩塞也。藏隐匿也。
问。小人閒居下文。特引曾子曰。十目所视。此只言恶之不可掩如此。而章句兼言善恶之不可掩。何欤。曰。人之为不善于幽独之中者。以为人不知之。然其诚中形外之不可掩。无异于十目之所视。十手之所指也。此固戒小人为恶之辞。而劝善之意。亦自在其中。故章句兼言善恶。以明君子必慎其独之意。
林启浚签论。小人之阴为恶而阳为善者。盖欲以诈善而掩其真恶也。然其善其恶。自有十手十目而不可掩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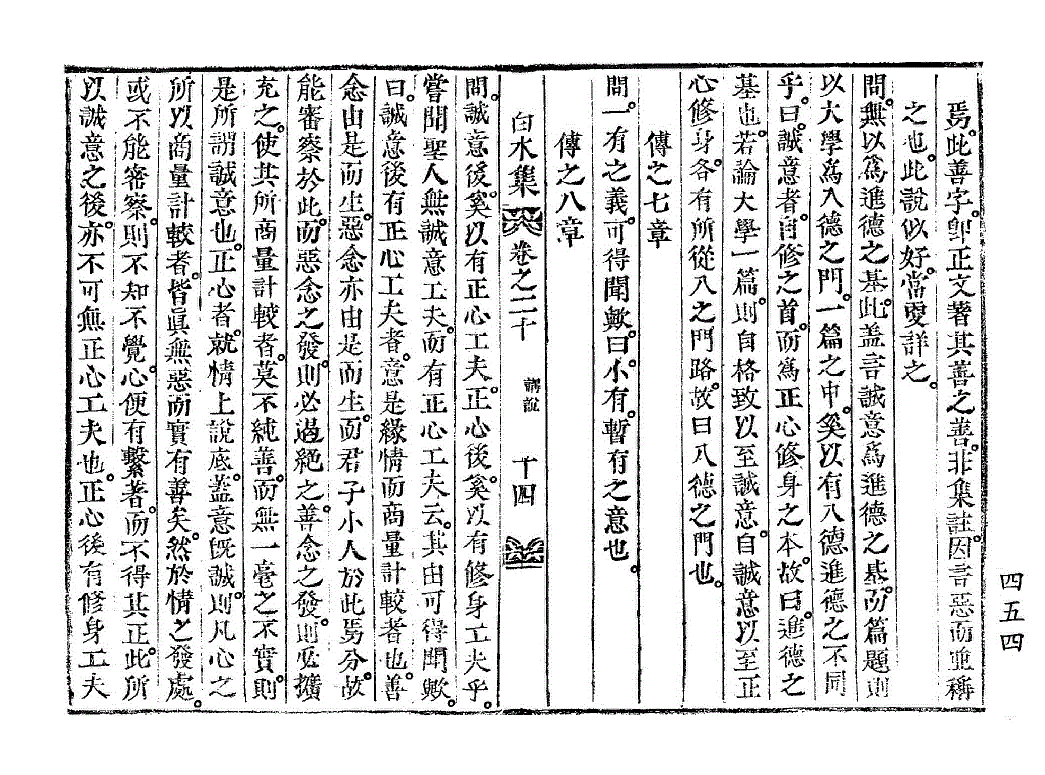 焉。此善字。即正文著其善之善。非集注。因言恶而并称之也。此说似好。当更详之。
焉。此善字。即正文著其善之善。非集注。因言恶而并称之也。此说似好。当更详之。问。无以为进德之基。此盖言诚意为进德之基。而篇题则以大学为入德之门。一篇之中。奚以有入德进德之不同乎。曰。诚意者。自修之首。而为正心修身之本。故曰。进德之基也。若论大学一篇。则自格致以至诚意。自诚意以至正心修身。各有所从入之门路。故曰入德之门也。
传之七章
问。一有之义。可得闻欤。曰。小有。暂有之意也。
传之八章
问。诚意后。奚以有正心工夫。正心后。奚以有修身工夫乎。尝闻圣人无诚意工夫。而有正心工夫云。其由可得闻欤。曰。诚意后有正心工夫者。意是缘情而商量计较者也。善念由是而生。恶念亦由是而生。而君子小人于此焉分。故能审察于此。而恶念之发。则必遏绝之。善念之发。则必扩充之。使其所商量计较者。莫不纯善。而无一毫之不实。则是所谓诚意也。正心者。就情上说底。盖意既诚。则凡心之所以商量计较者。皆真无恶而实有善矣。然于情之发处。或不能密察。则不知不觉。心便有系著。而不得其正。此所以诚意之后。亦不可无正心工夫也。正心后有修身工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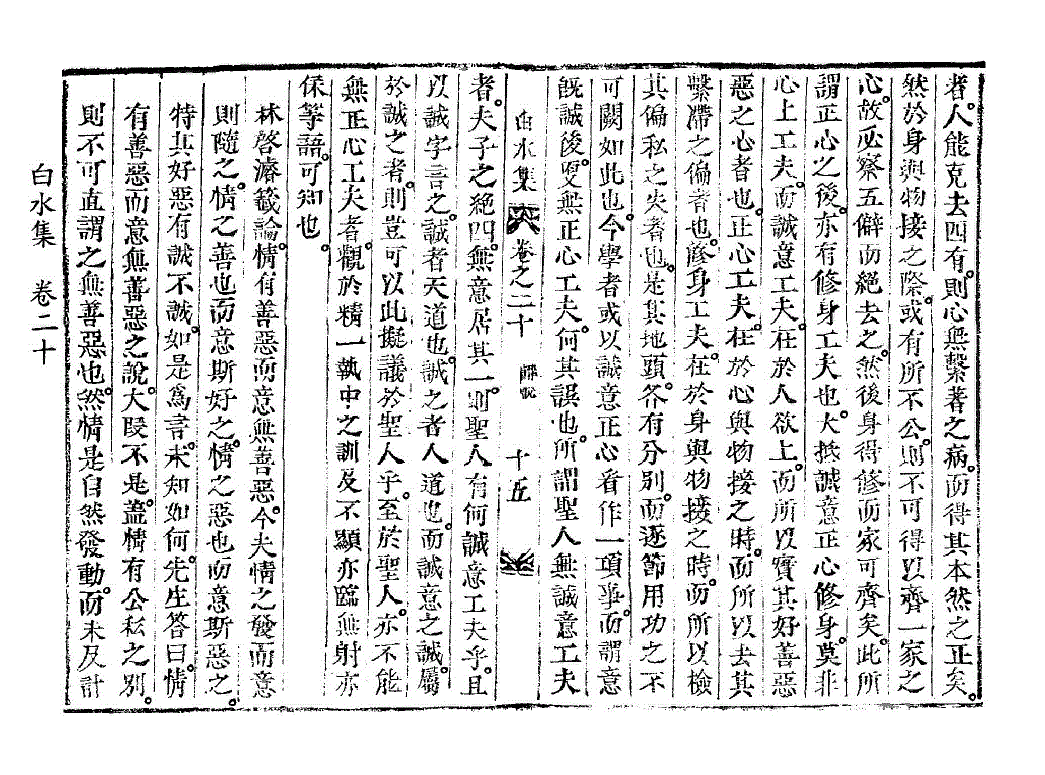 者。人能克去四有。则心无系著之病。而得其本然之正矣。然于身与物接之际。或有所不公。则不可得以齐一家之心。故必察五僻而绝去之。然后身得修而家可齐矣。此所谓正心之后。亦有修身工夫也。大抵诚意正心修身。莫非心上工夫。而诚意工夫。在于人欲上。而所以实其好善恶恶之心者也。正心工夫。在于心与物接之时。而所以去其系滞之偏者也。修身工夫。在于身与物接之时。而所以检其偏私之失者也。是其地头。各有分别。而逐节用功之不可阙如此也。今学者或以诚意正心看作一项事。而谓意既诚后。更无正心工夫。何其误也。所谓圣人无诚意工夫者。夫子之绝四。无意居其一。则圣人有何诚意工夫乎。且以诚字言之。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而诚意之诚。属于诚之者。则岂可以此拟议于圣人乎。至于圣人。亦不能无正心工夫者。观于精一执中之训及不显亦临无射亦保等语。可知也。
者。人能克去四有。则心无系著之病。而得其本然之正矣。然于身与物接之际。或有所不公。则不可得以齐一家之心。故必察五僻而绝去之。然后身得修而家可齐矣。此所谓正心之后。亦有修身工夫也。大抵诚意正心修身。莫非心上工夫。而诚意工夫。在于人欲上。而所以实其好善恶恶之心者也。正心工夫。在于心与物接之时。而所以去其系滞之偏者也。修身工夫。在于身与物接之时。而所以检其偏私之失者也。是其地头。各有分别。而逐节用功之不可阙如此也。今学者或以诚意正心看作一项事。而谓意既诚后。更无正心工夫。何其误也。所谓圣人无诚意工夫者。夫子之绝四。无意居其一。则圣人有何诚意工夫乎。且以诚字言之。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而诚意之诚。属于诚之者。则岂可以此拟议于圣人乎。至于圣人。亦不能无正心工夫者。观于精一执中之训及不显亦临无射亦保等语。可知也。林启浚签论。情有善恶而意无善恶。今夫情之发而意则随之。情之善也而意斯好之。情之恶也而意斯恶之。特其好恶有诚不诚。如是为言。未知如何。先生答曰。情有善恶而意无善恶之说。大段不是。盖情有公私之别。则不可直谓之无善恶也。然情是自然发动。而未及计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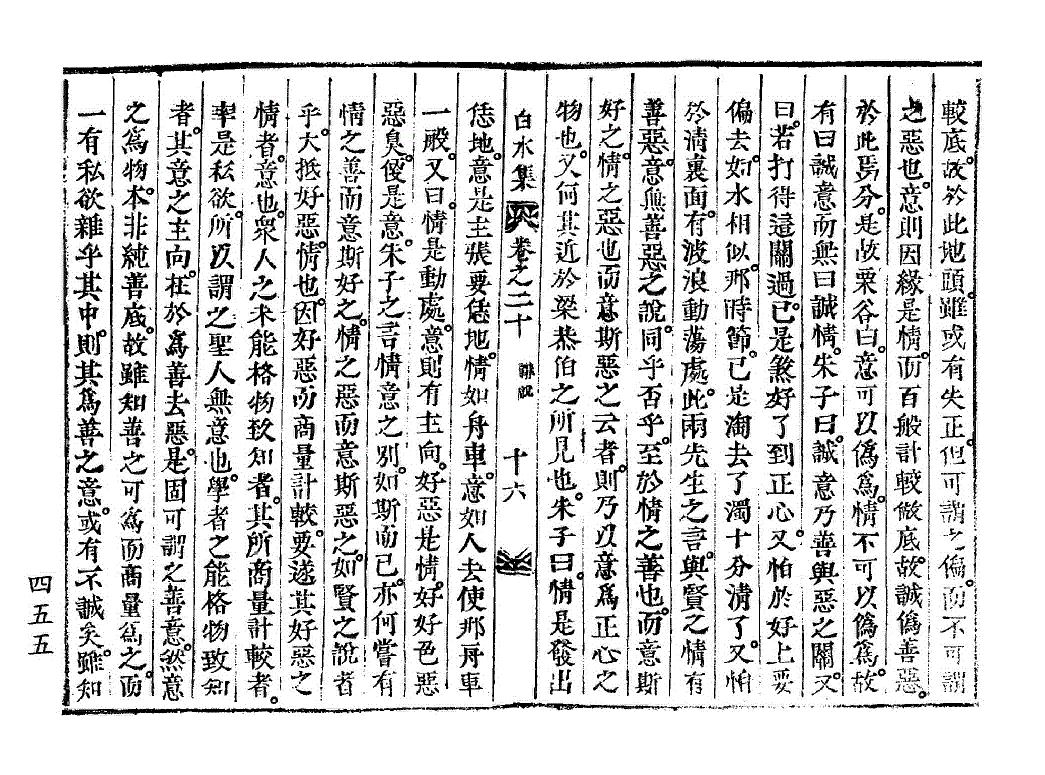 较底。故于此地头。虽或有失正。但可谓之偏。而不可谓之恶也。意则因缘是情。而百般计较做底。故诚伪善恶。于此焉分。是故栗谷曰。意可以伪为。情不可以伪为。故有曰诚意而无曰诚情。朱子曰。诚意乃善与恶之关。又曰。若打得这关过。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此两先生之言。与贤之情有善恶。意无善恶之说。同乎否乎。至于情之善也。而意斯好之。情之恶也而意斯恶之云者。则乃以意为正心之物也。又何其近于梁恭伯之所见也。朱子曰。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又曰。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朱子之言情意之别。如斯而已。亦何尝有情之善而意斯好之。情之恶而意斯恶之。如贤之说者乎。大抵好恶。情也。因好恶而商量计较。要遂其好恶之情者。意也。众人之未能格物致知者。其所商量计较者。率是私欲。所以谓之圣人无意也。学者之能格物致知者。其意之主向。在于为善去恶。是固可谓之善意。然意之为物。本非纯善底。故虽知善之可为而商量为之。而一有私欲杂乎其中。则其为善之意。或有不诚矣。虽知
较底。故于此地头。虽或有失正。但可谓之偏。而不可谓之恶也。意则因缘是情。而百般计较做底。故诚伪善恶。于此焉分。是故栗谷曰。意可以伪为。情不可以伪为。故有曰诚意而无曰诚情。朱子曰。诚意乃善与恶之关。又曰。若打得这关过。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此两先生之言。与贤之情有善恶。意无善恶之说。同乎否乎。至于情之善也。而意斯好之。情之恶也而意斯恶之云者。则乃以意为正心之物也。又何其近于梁恭伯之所见也。朱子曰。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又曰。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朱子之言情意之别。如斯而已。亦何尝有情之善而意斯好之。情之恶而意斯恶之。如贤之说者乎。大抵好恶。情也。因好恶而商量计较。要遂其好恶之情者。意也。众人之未能格物致知者。其所商量计较者。率是私欲。所以谓之圣人无意也。学者之能格物致知者。其意之主向。在于为善去恶。是固可谓之善意。然意之为物。本非纯善底。故虽知善之可为而商量为之。而一有私欲杂乎其中。则其为善之意。或有不诚矣。虽知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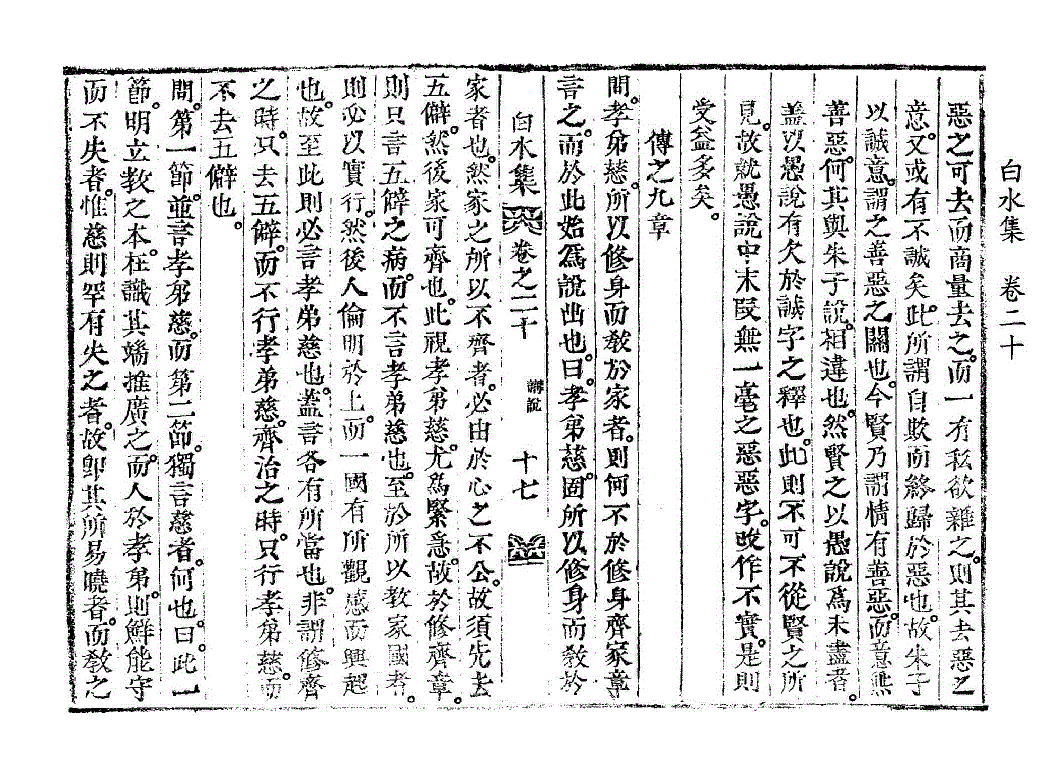 恶之可去而商量去之。而一有私欲杂之。则其去恶之意。又或有不诚矣。此所谓自欺而终归于恶也。故朱子以诚意。谓之善恶之关也。今贤乃谓情有善恶。而意无善恶。何其与朱子说。相违也。然贤之以愚说为未尽者。盖以愚说有欠于诚字之释也。此则不可不从贤之所见。故就愚说中末段无一毫之恶恶字。改作不实。是则受益多矣。
恶之可去而商量去之。而一有私欲杂之。则其去恶之意。又或有不诚矣。此所谓自欺而终归于恶也。故朱子以诚意。谓之善恶之关也。今贤乃谓情有善恶。而意无善恶。何其与朱子说。相违也。然贤之以愚说为未尽者。盖以愚说有欠于诚字之释也。此则不可不从贤之所见。故就愚说中末段无一毫之恶恶字。改作不实。是则受益多矣。传之九章
问。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则何不于修身齐家章言之。而于此始为说出也。曰。孝弟慈。固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家之所以不齐者。必由于心之不公。故须先去五僻。然后家可齐也。此视孝弟慈。尤为紧急。故于修齐章。则只言五僻之病。而不言孝弟慈也。至于所以教家国者。则必以实行。然后人伦明于上。而一国有所观感而兴起也。故至此则必言孝弟慈也。盖言各有所当也。非谓修齐之时。只去五僻。而不行孝弟慈。齐治之时。只行孝弟慈。而不去五僻也。
问。第一节。并言孝弟慈。而第二节。独言慈者。何也。曰。此一节。明立教之本。在识其端推广之。而人于孝弟。则鲜能守而不失者。惟慈则罕有失之者。故即其所易晓者。而教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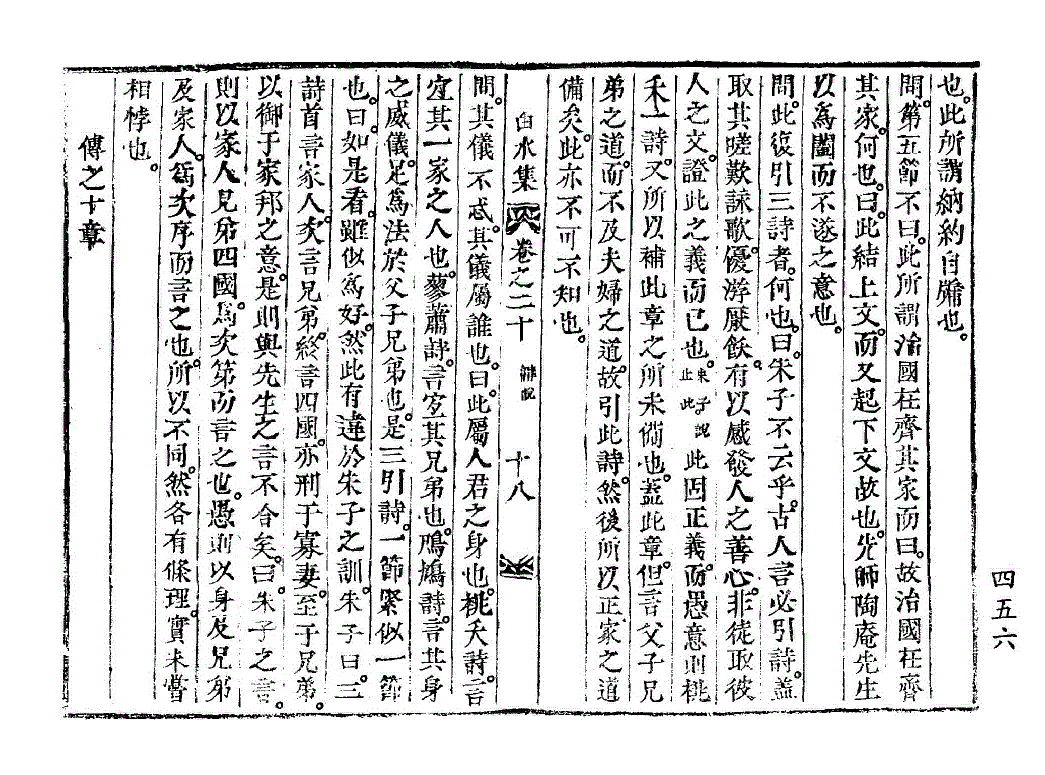 也。此所谓纳约自牖也。
也。此所谓纳约自牖也。问。第五节不曰。此所谓治国在齐其家而曰。故治国在齐其家。何也。曰。此结上文。而又起下文故也。先师陶庵先生以为阖而不遂之意也。
问。此复引三诗者。何也。曰。朱子不云乎。古人言必引诗。盖取其嗟叹咏歌。优游厌饫。有以感发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人之文。證此之义而已也。(朱子说止此。)此固正义。而愚意则桃夭一诗。又所以补此章之所未备也。盖此章。但言父子兄弟之道。而不及夫妇之道。故引此诗。然后所以正家之道备矣。此亦不可不知也。
问。其仪不忒。其仪属谁也。曰。此属人君之身也。桃夭诗。言宜其一家之人也。蓼萧诗。言宜其兄弟也。鸤鸠诗。言其身之威仪。足为法于父子兄弟也。是三引诗。一节紧似一节也。曰。如是看。虽似为好。然此有违于朱子之训。朱子曰。三诗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终言四国。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是则与先生之言不合矣。曰。朱子之言。则以家人兄弟四国。为次第而言之也。愚则以身及兄弟及家人。为次序而言之也。所以不同。然各有条理。实未尝相悖也。
传之十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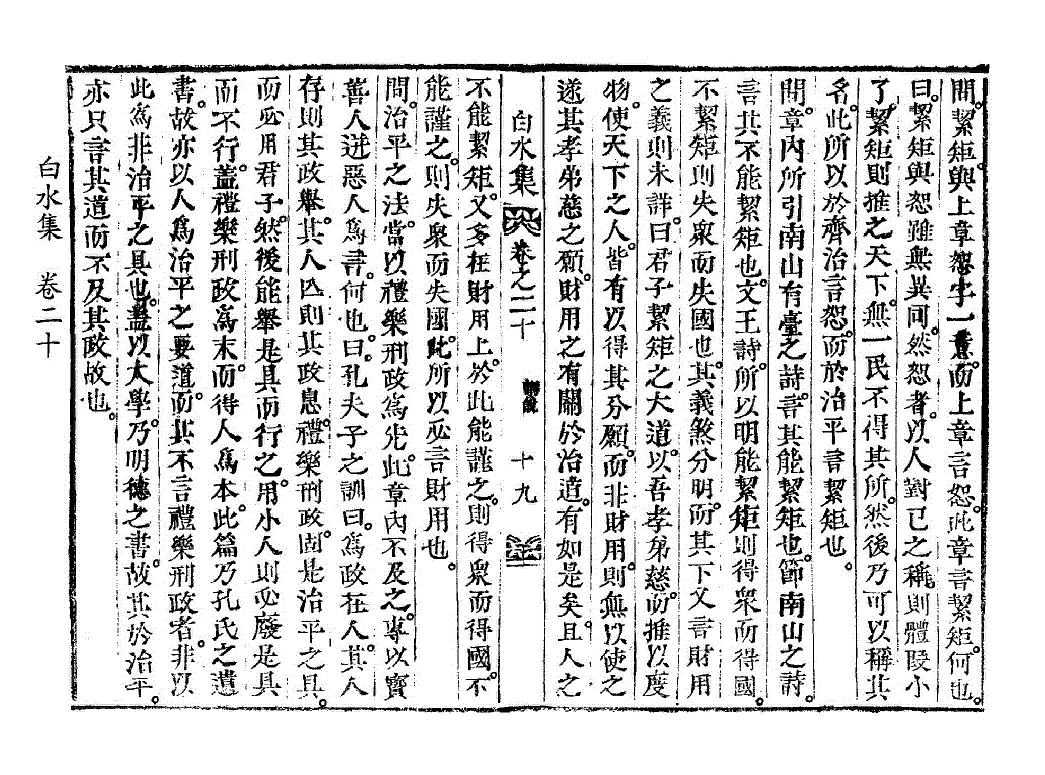 问。絜矩。与上章恕字一意。而上章言恕。此章言絜矩。何也。曰。絜矩与恕虽无异同。然恕者。以人对己之称。则体段小了。絜矩则推之天下。无一民不得其所。然后乃可以称其名。此所以于齐治言恕。而于治平言絜矩也。
问。絜矩。与上章恕字一意。而上章言恕。此章言絜矩。何也。曰。絜矩与恕虽无异同。然恕者。以人对己之称。则体段小了。絜矩则推之天下。无一民不得其所。然后乃可以称其名。此所以于齐治言恕。而于治平言絜矩也。问。章内所引南山有台之诗。言其能絜矩也。节南山之诗。言其不能絜矩也。文王诗。所以明能絜矩则得众而得国。不絜矩则失众而失国也。其义煞分明。而其下又言财用之义则未详。曰君子絜矩之大道。以吾孝弟慈。而推以度物。使天下之人。皆有以得其分愿。而非财用。则无以使之遂其孝弟慈之愿。财用之有关于治道。有如是矣。且人之不能絜矩。又多在财用上。于此能谨之。则得众而得国。不能谨之。则失众而失国。此所以必言财用也。
问。治平之法。当以礼乐刑政为先。此章内不及之。专以宝善人迸恶人为言。何也。曰。孔夫子之训曰。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乐刑政。固是治平之具。而必用君子。然后能举是具而行之。用小人则必废是具而不行。盖礼乐刑政为末。而得人为本。此篇乃孔氏之遗书。故亦以人为治平之要道。而其不言礼乐刑政者。非以此为非治平之具也。盖以大学。乃明德之书。故其于治平。亦只言其道而不及其政故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外集 第 4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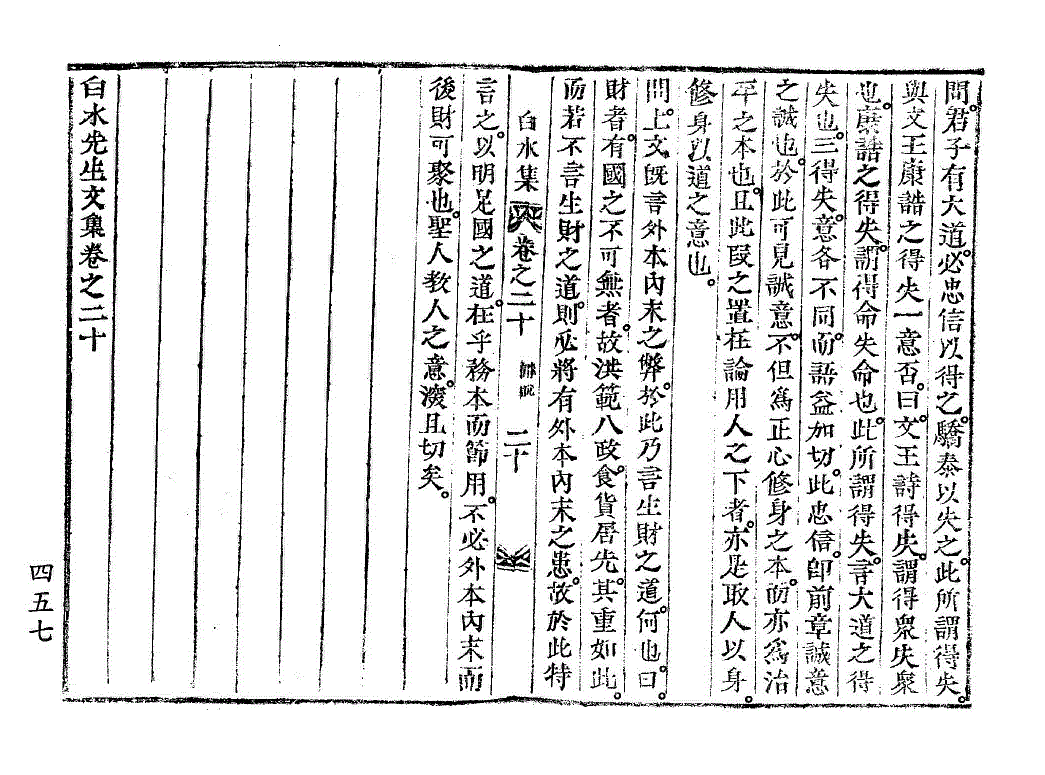 问。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此所谓得失。与文王康诰之得失一意否。曰。文王诗得失。谓得众失众也。康诰之得失。谓得命失命也。此所谓得失。言大道之得失也。三得失。意各不同。而语益加切。此忠信。即前章诚意之诚也。于此可见诚意。不但为正心修身之本。而亦为治平之本也。且此段之置在论用人之下者。亦是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之意也。
问。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此所谓得失。与文王康诰之得失一意否。曰。文王诗得失。谓得众失众也。康诰之得失。谓得命失命也。此所谓得失。言大道之得失也。三得失。意各不同。而语益加切。此忠信。即前章诚意之诚也。于此可见诚意。不但为正心修身之本。而亦为治平之本也。且此段之置在论用人之下者。亦是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之意也。问。上文既言外本内末之弊。于此乃言生财之道。何也。曰。财者。有国之不可无者。故洪范八政。食货居先。其重如此。而若不言生财之道。则必将有外本内末之患。故于此特言之。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用。不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圣人教人之意。深且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