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中庸讲说
中庸讲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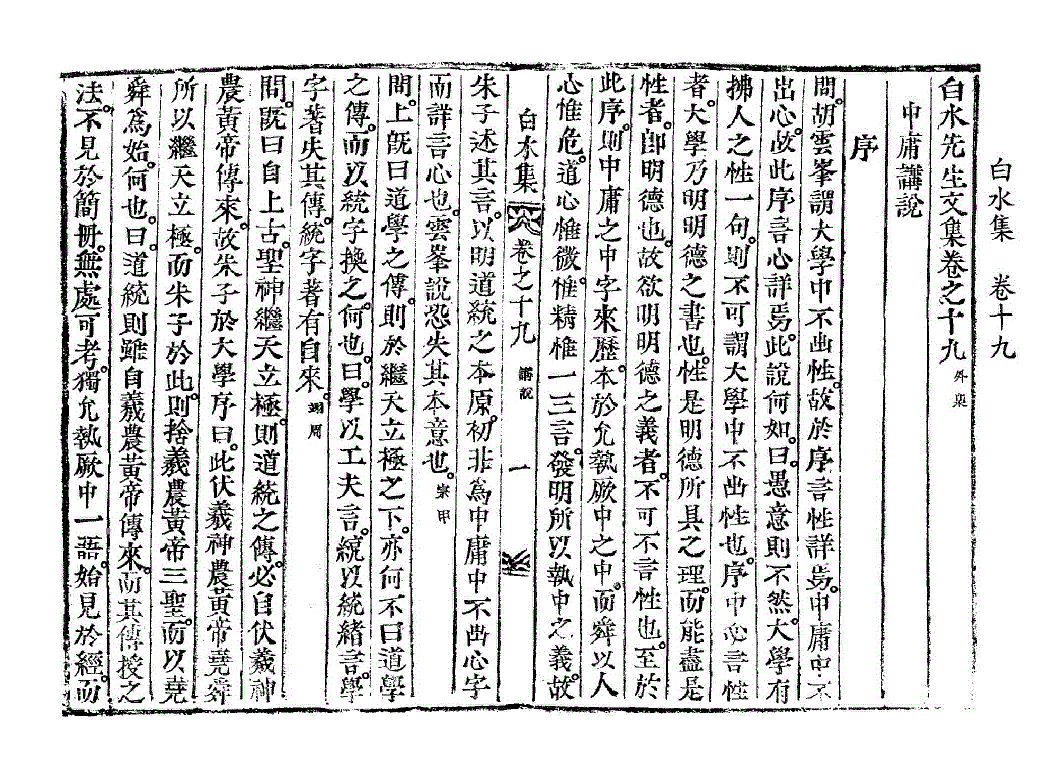 序
序问。胡云峰谓大学中不出性。故于序言性详焉。中庸中不出心。故此序言心详焉。此说何如。曰。愚意则不然。大学有拂人之性一句。则不可谓大学中不出性也。序中必言性者。大学乃明明德之书也。性是明德所具之理。而能尽是性者。即明德也。故欲明明德之义者。不可不言性也。至于此序。则中庸之中字来历。本于允执厥中之中。而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言。发明所以执中之义。故朱子述其言。以明道统之本原。初非为中庸中不出心字而详言心也。云峰说恐失其本意也。(宗甲)
问。上既曰道学之传。则于继天立极之下。亦何不曰道学之传。而以统字换之。何也。曰。学以工夫言。统以统绪言。学字著失其传。统字著有自来。(翊周)
问。既曰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则道统之传。必自伏羲神农黄帝传来。故朱子于大学序曰。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朱子于此。则舍羲农黄帝三圣。而以尧舜为始。何也。曰。道统则虽自羲农黄帝传来。而其传授之法。不见于简册。无处可考。独允执厥中一语。始见于经。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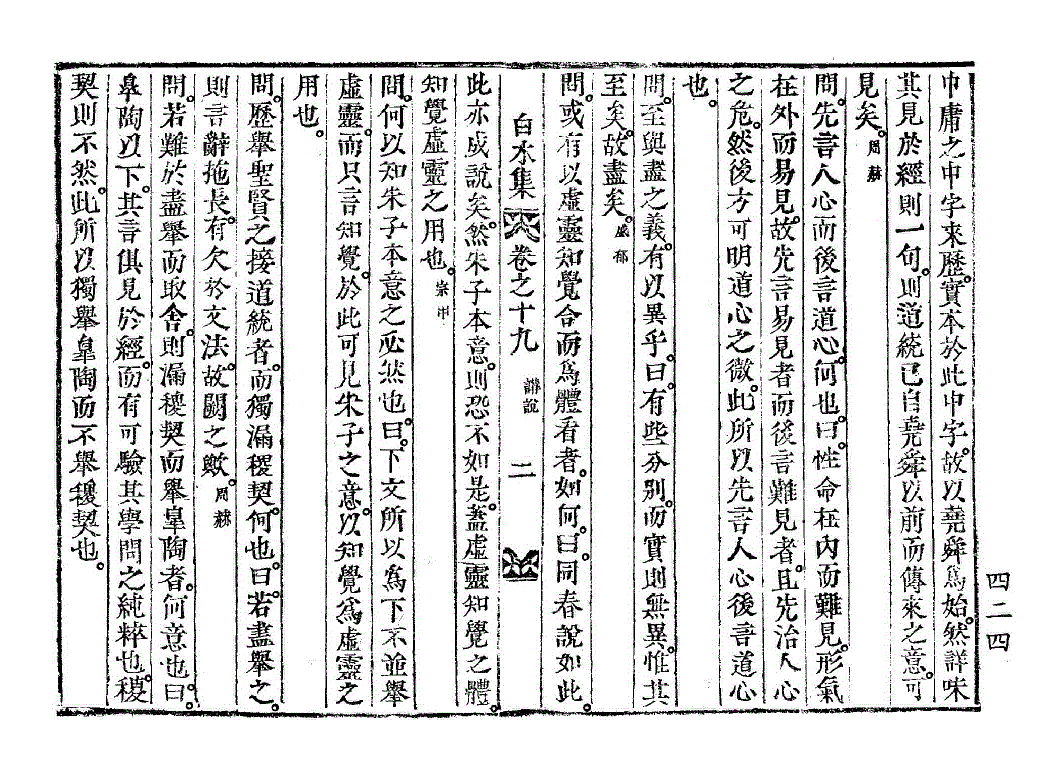 中庸之中字来历。实本于此中字。故以尧舜为始。然详味其见于经则一句。则道统已自尧舜以前而传来之意。可见矣。(周赫)
中庸之中字来历。实本于此中字。故以尧舜为始。然详味其见于经则一句。则道统已自尧舜以前而传来之意。可见矣。(周赫)问。先言人心而后言道心。何也。曰。性命在内而难见。形气在外而易见。故先言易见者而后言难见者。且先治人心之危。然后方可明道心之微。此所以先言人心后言道心也。
问。至与尽之义。有以异乎。曰。有些分别。而实则无异。惟其至矣。故尽矣。(盛郁)
问。或有以虚灵知觉合而为体看者。如何。曰。同春说如此。此亦成说矣。然朱子本意。则恐不如是。盖虚灵知觉之体。知觉虚灵之用也。(宗甲)
问。何以知朱子本意之必然也。曰。下文所以为下不并举虚灵。而只言知觉。于此可见朱子之意。以知觉为虚灵之用也。
问。历举圣贤之接道统者。而独漏稷契。何也。曰。若尽举之。则言辞拖长。有欠于文法。故阙之欤。(周赫)
问。若难于尽举而取舍。则漏稷契而举皋陶者。何意也。曰。皋陶以下。其言俱见于经。而有可验其学问之纯粹也。稷契则不然。此所以独举皋陶而不举稷契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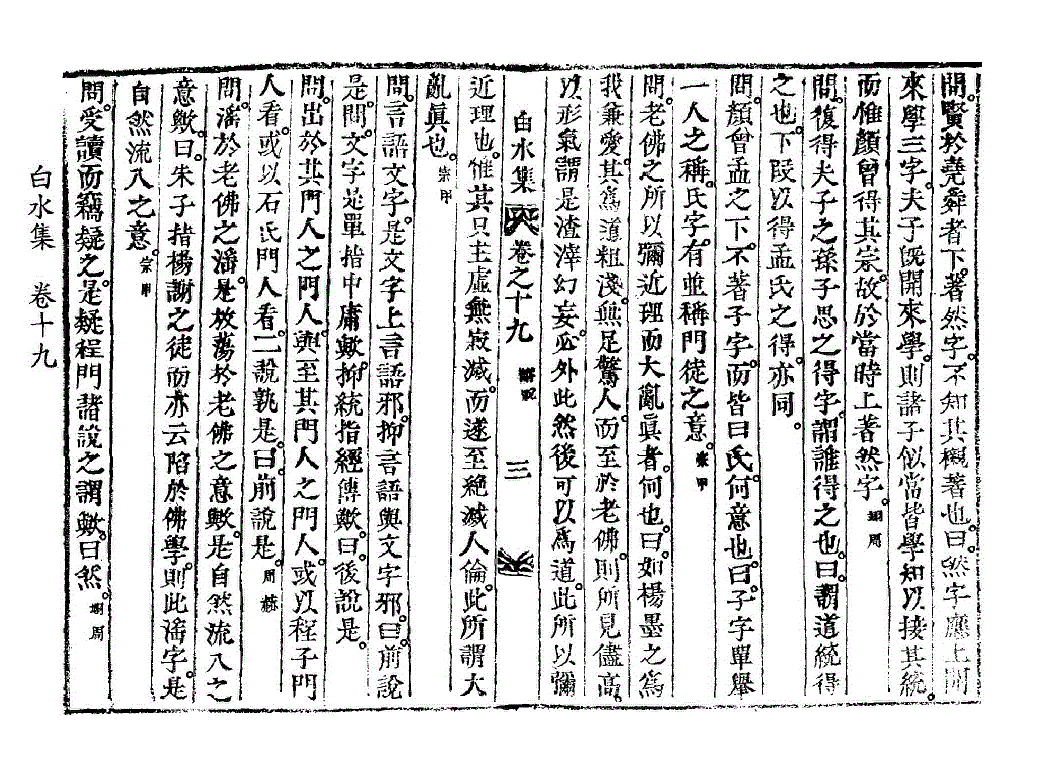 问。贤于尧舜者下。著然字。不知其衬著也。曰。然字应上开来学三字。夫子既开来学。则诸子似当皆学知以接其统。而惟颜曾得其宗。故于当时上著然字。(翊周)
问。贤于尧舜者下。著然字。不知其衬著也。曰。然字应上开来学三字。夫子既开来学。则诸子似当皆学知以接其统。而惟颜曾得其宗。故于当时上著然字。(翊周)问。复得夫子之孙子思之得字。谓谁得之也。曰。谓道统得之也。下段以得孟氏之得。亦同。
问。颜曾孟之下。不著子字。而皆曰氏。何意也。曰。子字单举一人之称。氏字。有并称门徒之意。(宗甲)
问。老佛之所以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何也。曰。如杨墨之为我兼爱。其为道粗浅。无足惊人。而至于老佛。则所见尽高。以形气谓是渣滓幻妄。必外此然后可以为道。此所以弥近理也。惟其只主虚无寂灭。而遂至绝灭人伦。此所谓大乱真也。(宗甲)
问。言语文字。是文字上言语邪。抑言语与文字邪。曰。前说是。问。文字是单指中庸欤。抑统指经传欤。曰。后说是。
问。出于其门人之门人。与至其门人之门人。或以程子门人看。或以石氏门人看。二说孰是。曰。前说是。(周赫)
问。淫于老佛之淫。是放荡于老佛之意欤。是自然流入之意欤。曰。朱子指杨谢之徒而亦云陷于佛学。则此淫字。是自然流入之意。(宗甲)
问。受读而窃疑之。是疑程门诸说之谓欤。曰然。(翊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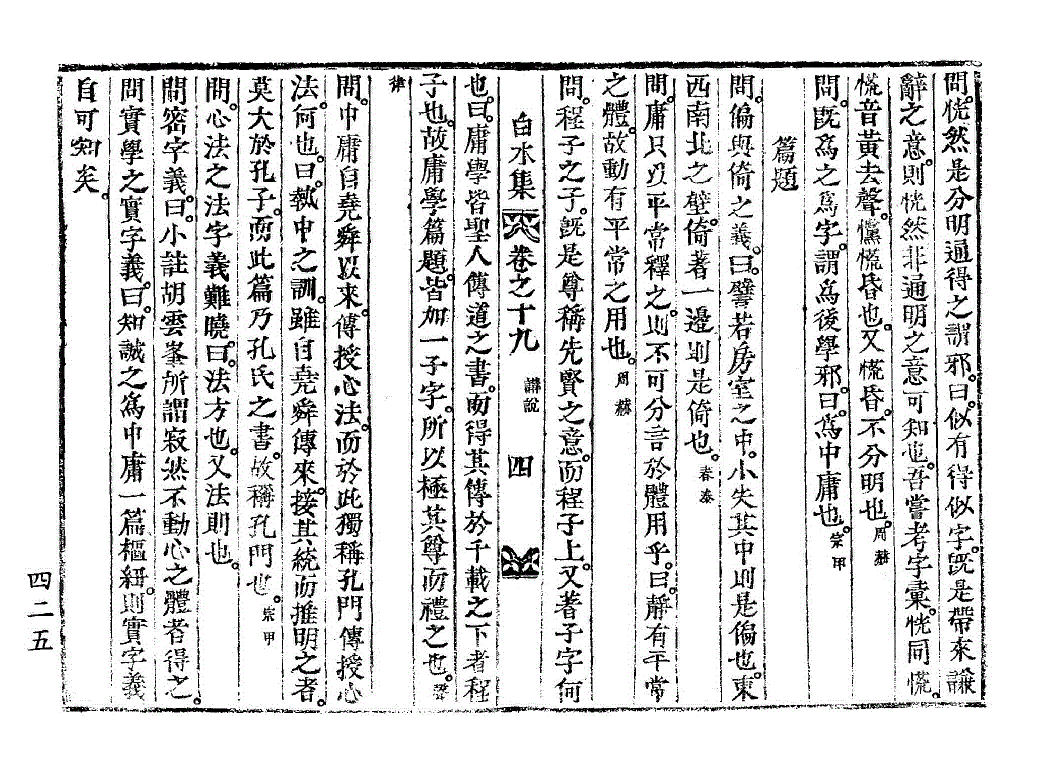 问。恍然是分明通得之谓邪。曰。似有得似字。既是带来谦辞之意。则恍然非通明之意可知也。吾尝考字汇。恍同慌。慌音黄去声。惝慌昏也。又慌昏。不分明也。(周赫)
问。恍然是分明通得之谓邪。曰。似有得似字。既是带来谦辞之意。则恍然非通明之意可知也。吾尝考字汇。恍同慌。慌音黄去声。惝慌昏也。又慌昏。不分明也。(周赫)问。既为之为字。谓为后学邪。曰。为中庸也。(宗甲)
篇题
问。偏与倚之义。曰。譬若房室之中。小失其中则是偏也。东西南北之壁。倚著一边则是倚也。(春泰)
问。庸只以平常释之。则不可分言于体用乎。曰。静有平常之体。故动有平常之用也。(周赫)
问。程子之子。既是尊称先贤之意。而程子上。又著子字何也。曰。庸学皆圣人传道之书。而得其传于千载之下者程子也。故庸学篇题。皆加一子字。所以极其尊而礼之也。(声律)
问。中庸自尧舜以来。传授心法。而于此独称孔门传授心法。何也。曰。执中之训。虽自尧舜传来。接其统而推明之者。莫大于孔子。而此篇乃孔氏之书。故称孔门也。(宗甲)
问。心法之法字义难晓。曰。法方也。又法则也。
问密字义。曰。小注胡云峰所谓寂然不动心之体者得之。
问实学之实字义。曰。知诚之为中庸一篇枢纽。则实字义自可知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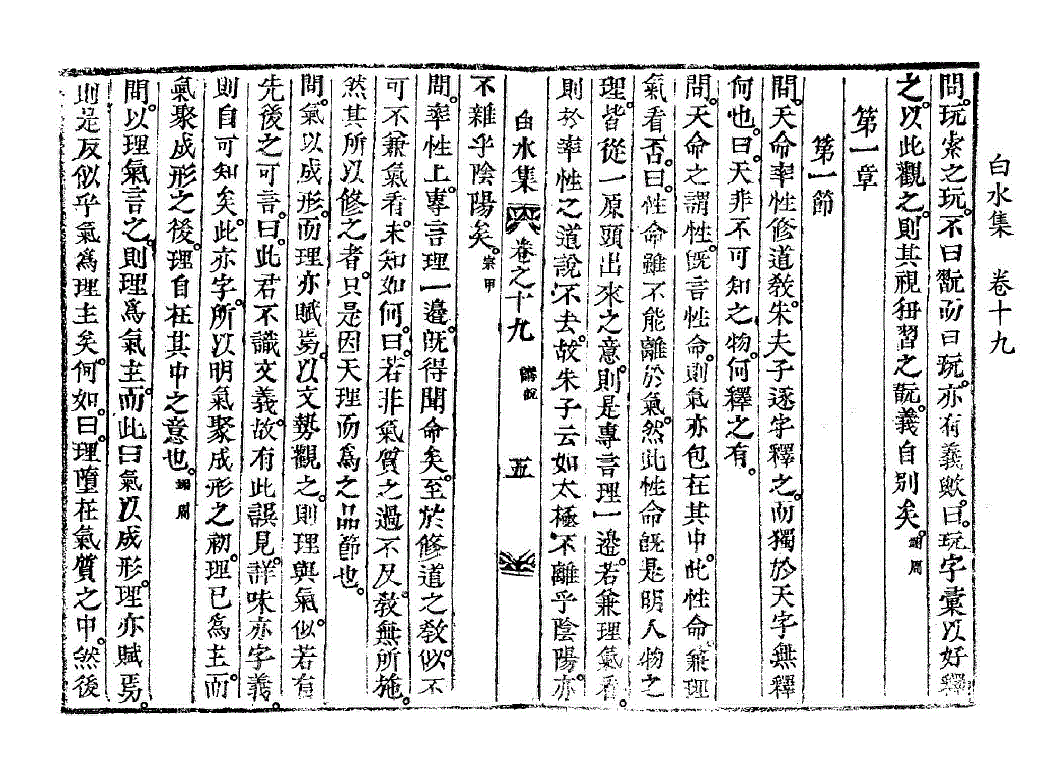 问。玩索之玩。不曰玩而曰玩。亦有义欤。曰。玩字汇以好释之。以此观之。则其视狃习之玩。义自别矣。(翊周)
问。玩索之玩。不曰玩而曰玩。亦有义欤。曰。玩字汇以好释之。以此观之。则其视狃习之玩。义自别矣。(翊周)第一章
第一节
问。天命率性修道教。朱夫子逐字释之。而独于天字无释何也。曰。天非不可知之物。何释之有。
问。天命之谓性。既言性命。则气亦包在其中。此性命。兼理气看否。曰。性命虽不能离于气。然此性命既是明人物之理。皆从一原头出来之意。则是专言理一边。若兼理气看。则于率性之道说不去。故朱子云如太极不离乎阴阳。亦不杂乎阴阳矣。(宗甲)
问。率性上。专言理一边。既得闻命矣。至于修道之教。似不可不兼气看。未知如何。曰。若非气质之过不及。教无所施。然其所以修之者。只是因天理而为之品节也。
问。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以文势观之。则理与气。似若有先后之可言。曰。此君不识文义。故有此误见。详味亦字义。则自可知矣。此亦字。所以明气聚成形之初。理已为主。而气聚成形之后。理自在其中之意也。(翊周)
问。以理气言之。则理为气主。而此曰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则是反似乎气为理主矣。何如。曰。理堕在气质之中。然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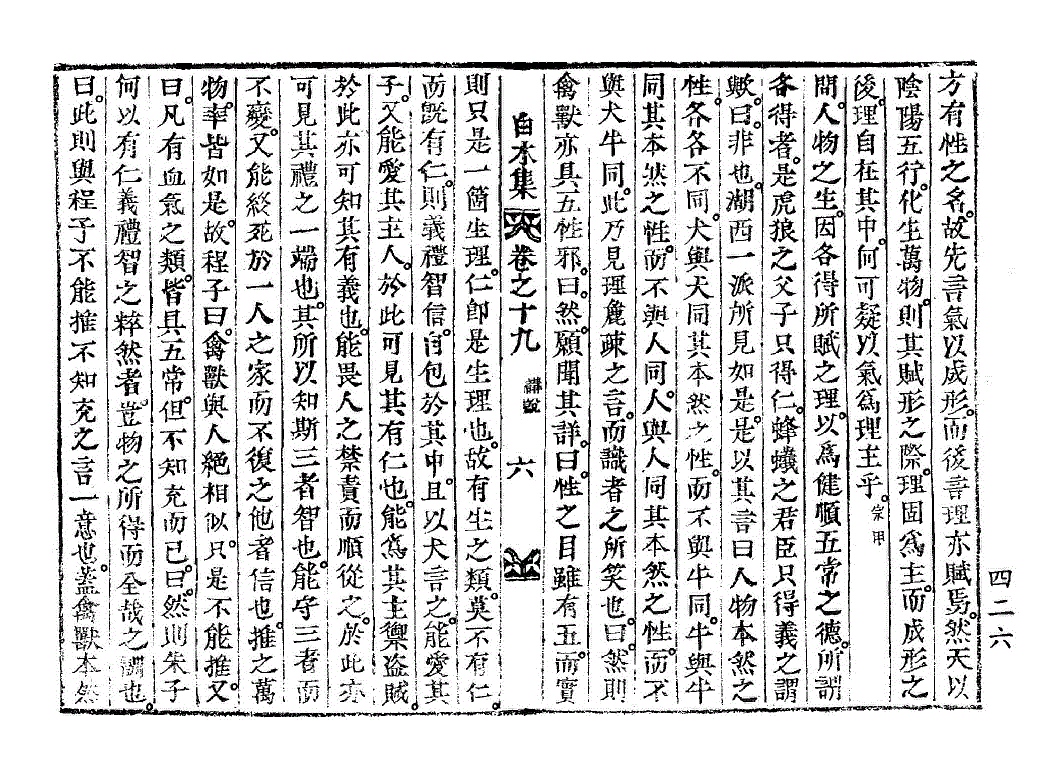 方有性之名。故先言气以成形。而后言理亦赋焉。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则其赋形之际。理固为主。而成形之后。理自在其中。何可疑以气为理主乎。(宗甲)
方有性之名。故先言气以成形。而后言理亦赋焉。然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则其赋形之际。理固为主。而成形之后。理自在其中。何可疑以气为理主乎。(宗甲)问。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各得者。是虎狼之父子只得仁。蜂蚁之君臣只得义之谓欤。曰。非也。湖西一派所见如是。是以其言曰人物本然之性。各各不同。犬与犬同其本然之性。而不与牛同。牛与牛同其本然之性。而不与人同。人与人同其本然之性。而不与犬牛同。此乃见理粗疏之言。而识者之所笑也。曰。然则禽兽亦具五性邪。曰。然。愿闻其详。曰。性之目虽有五。而实则只是一个生理。仁即是生理也。故有生之类。莫不有仁。而既有仁。则义礼智信。自包于其中。且以犬言之。能爱其子。又能爱其主人。于此可见其有仁也。能为其主御盗贼。于此亦可知其有义也。能畏人之禁责而顺从之。于此亦可见其礼之一端也。其所以知斯三者智也。能守三者而不变。又能终死于一人之家而不复之他者信也。推之万物。率皆如是。故程子曰。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又曰。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曰。然则朱子何以有仁义礼智之粹然者。岂物之所得而全哉之训也。曰。此则与程子不能推不知充之言一意也。盖禽兽本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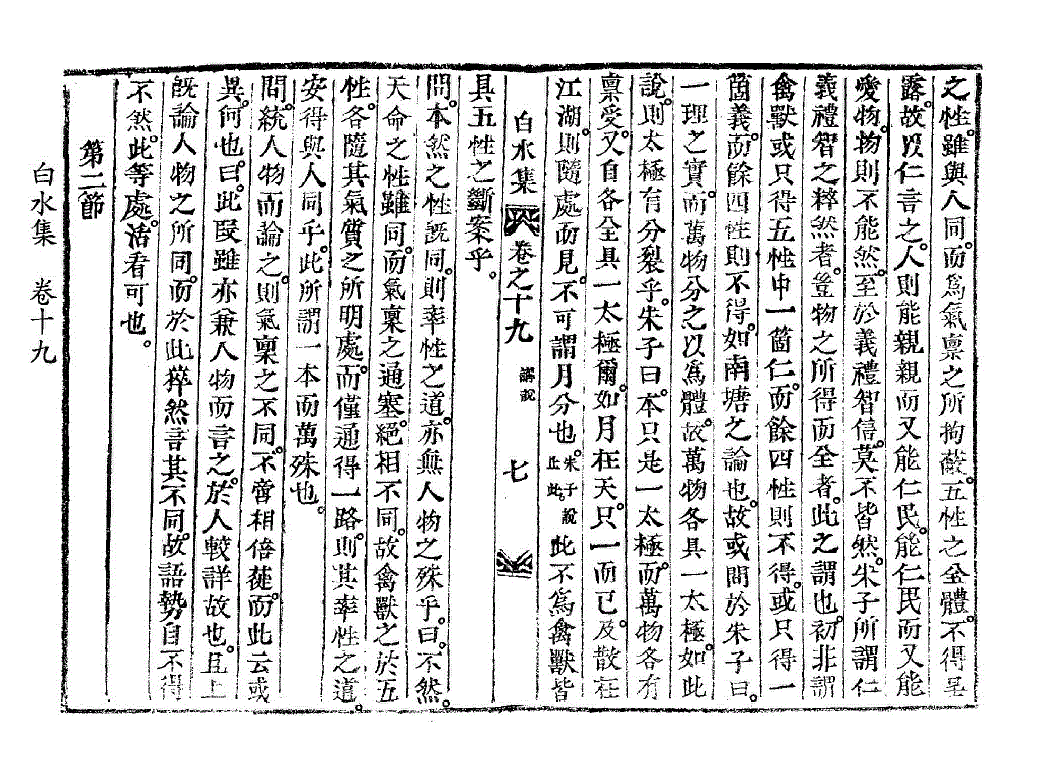 之性。虽与人同。而为气禀之所拘蔽。五性之全体。不得呈露。故以仁言之。人则能亲亲而又能仁民。能仁民而又能爱物。物则不能然。至于义礼智信。莫不皆然。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之粹然者。岂物之所得而全者。此之谓也。初非谓禽兽或只得五性中一个仁。而馀四性则不得。或只得一个义。而馀四性则不得。如南塘之论也。故或问于朱子曰。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太极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朱子说止此。)此不为禽兽皆具五性之断案乎。
之性。虽与人同。而为气禀之所拘蔽。五性之全体。不得呈露。故以仁言之。人则能亲亲而又能仁民。能仁民而又能爱物。物则不能然。至于义礼智信。莫不皆然。朱子所谓仁义礼智之粹然者。岂物之所得而全者。此之谓也。初非谓禽兽或只得五性中一个仁。而馀四性则不得。或只得一个义。而馀四性则不得。如南塘之论也。故或问于朱子曰。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太极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朱子说止此。)此不为禽兽皆具五性之断案乎。问。本然之性既同。则率性之道。亦无人物之殊乎。曰。不然。天命之性虽同。而气禀之通塞。绝相不同。故禽兽之于五性。各随其气质之所明处。而仅通得一路。则其率性之道。安得与人同乎。此所谓一本而万殊也。
问。统人物而论之。则气禀之不同。不啻相倍蓰。而此云或异。何也。曰。此段虽亦兼人物而言之。于人较详故也。且上既论人物之所同。而于此猝然言其不同。故语势自不得不然。此等处。活看可也。
第二节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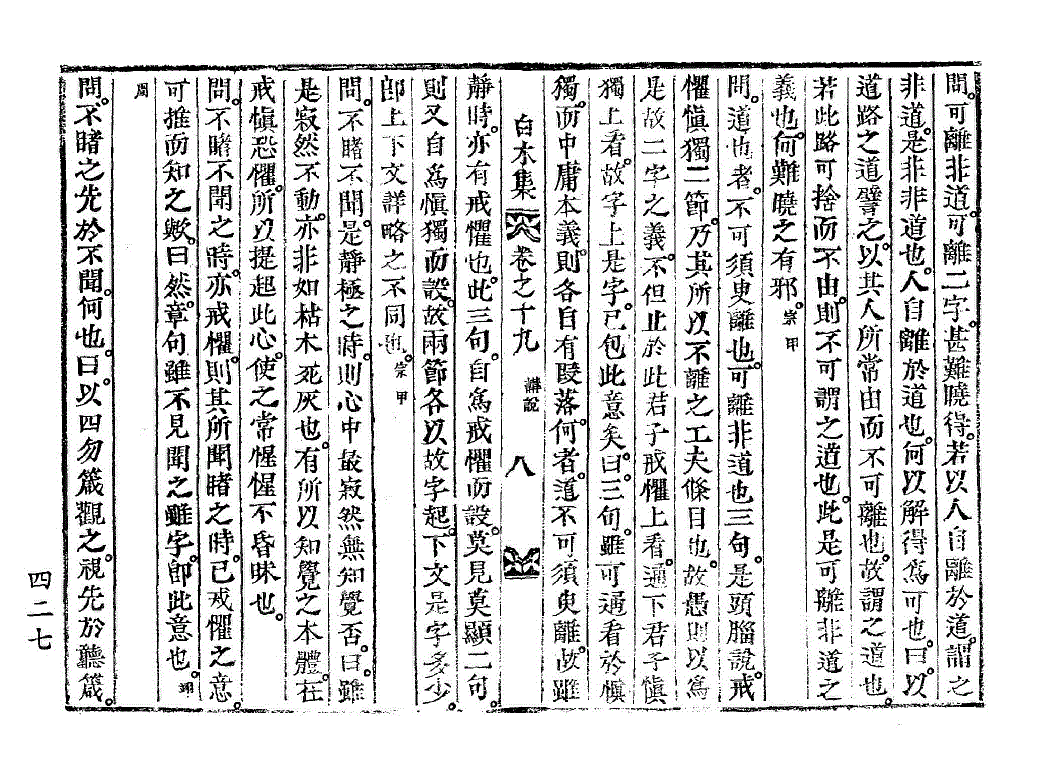 问。可离非道。可离二字。甚难晓得。若以人自离于道。谓之非道。是非非道也。人自离于道也。何以解得为可也。曰。以道路之道譬之。以其人所常由而不可离也。故谓之道也。若此路可舍而不由。则不可谓之道也。此是可离非道之义也。何难晓之有邪。(宗甲)
问。可离非道。可离二字。甚难晓得。若以人自离于道。谓之非道。是非非道也。人自离于道也。何以解得为可也。曰。以道路之道譬之。以其人所常由而不可离也。故谓之道也。若此路可舍而不由。则不可谓之道也。此是可离非道之义也。何难晓之有邪。(宗甲)问。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三句。是头脑说。戒惧慎独二节。乃其所以不离之工夫条目也。故愚则以为是故二字之义。不但止于此君子戒惧上看。通下君子慎独上看。故字上是字。已包此意矣。曰。三句。虽可通看于慎独。而中庸本义。则各自有段落。何者。道不可须臾离。故虽静时。亦有戒惧也。此三句。自为戒惧而设。莫见莫显二句。则又自为慎独而设。故两节各以故字起。下文是字多少。即上下文详略之不同也。(宗甲)
问。不睹不闻。是静极之时。则心中最寂然无知觉否。曰。虽是寂然不动。亦非如枯木死灰也。有所以知觉之本体。在戒慎恐惧。所以提起此心。使之常惺惺不昏昧也。
问。不睹不闻之时。亦戒惧。则其所闻睹之时。已戒惧之意。可推而知之欤。曰然。章句虽不见闻之虽字。即此意也。(翊周)
问。不睹之先于不闻。何也。曰。以四勿箴观之。视先于听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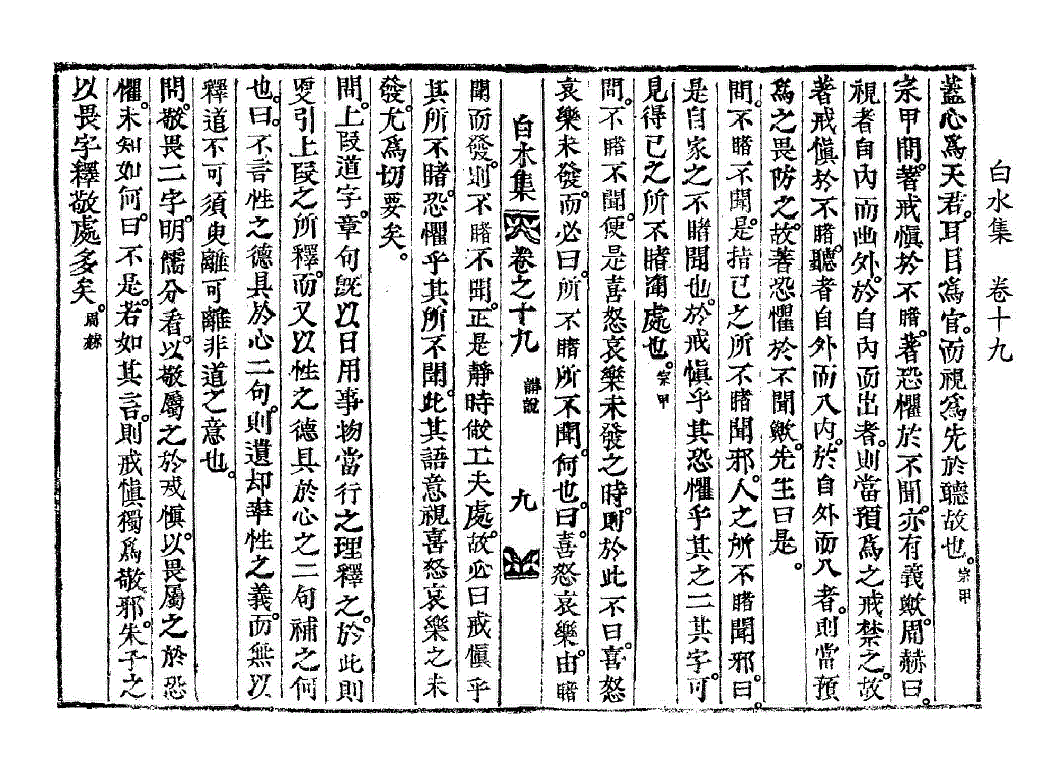 盖心为天君。耳目为官。而视为先于听故也。(宗甲)
盖心为天君。耳目为官。而视为先于听故也。(宗甲)宗甲问。著戒慎于不睹。著恐惧于不闻。亦有义欤。周赫曰。视者自内而出外。于自内而出者。则当预为之戒禁之。故著戒慎于不睹。听者自外而入内。于自外而入者。则当预为之畏防之。故著恐惧于不闻欤。先生曰是。
问。不睹不闻。是指己之所不睹闻邪。人之所不睹闻邪。曰。是自家之不睹闻也。于戒慎乎其恐惧乎其之二其字。可见得己之所不睹闻处也。(宗甲)
问。不睹不闻。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则于此不曰。喜怒哀乐未发。而必曰。所不睹所不闻。何也。曰。喜怒哀乐。由睹闻而发。则不睹不闻。正是静时做工夫处。故必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其语意视喜怒哀乐之未发。尤为切要矣。
问。上段道字。章句既以日用事物当行之理释之。于此则更引上段之所释。而又以性之德具于心之二句补之何也。曰。不言性之德具于心二句。则遗却率性之义。而无以释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之意也。
问。敬畏二字。明儒分看。以敬属之于戒慎。以畏属之于恐惧。未知如何。曰不是。若如其言。则戒慎独为敬邪。朱子之以畏字释敬处多矣。(周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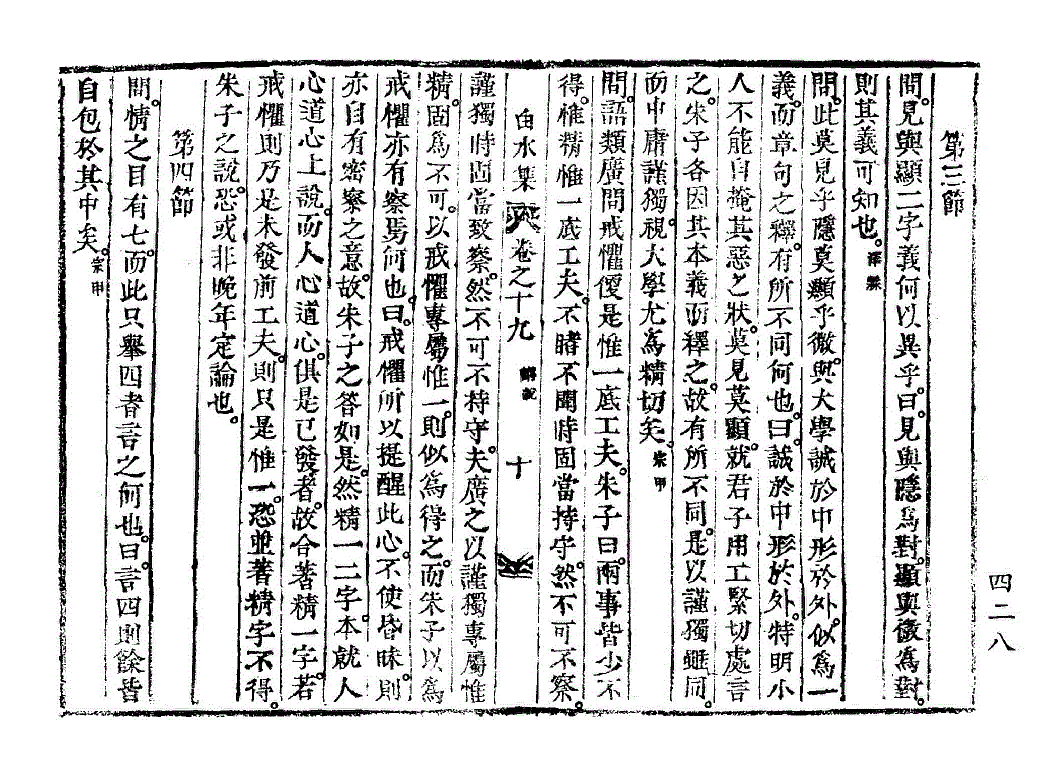 第三节
第三节问。见与显二字义何以异乎。曰。见与隐为对。显与微为对。则其义可知也。(泽霖)
问。此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与大学诚于中形于外。似为一义。而章句之释。有所不同何也。曰。诚于中形于外。特明小人不能自掩其恶之状。莫见莫显。就君子用工紧切处言之。朱子各因其本义而释之。故有所不同。是以谨独虽同。而中庸谨独。视大学尤为精切矣。(宗甲)
问。语类广问戒惧便是惟一底工夫。朱子曰。两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闻时固当持守。然不可不察。谨独时固当致察。然不可不持守。夫广之以谨独专属惟精。固为不可。以戒惧专属惟一。则似为得之。而朱子以为戒惧亦有察焉何也。曰。戒惧所以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则亦自有密察之意。故朱子之答如是。然精一二字。本就人心道心上说。而人心道心。俱是已发者。故合著精一字。若戒惧则乃是未发前工夫。则只是惟一。恐并著精字不得。朱子之说。恐或非晚年定论也。
第四节
问。情之目有七。而此只举四者言之何也。曰。言四则馀皆自包于其中矣。(宗甲)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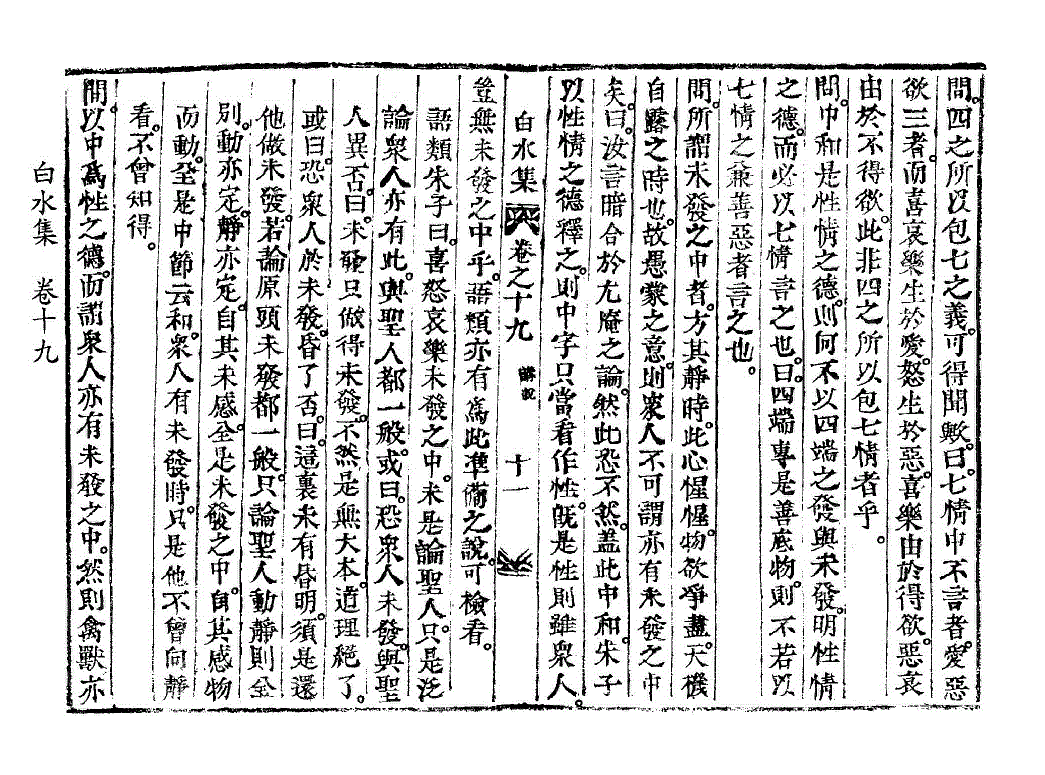 问。四之所以包七之义。可得闻欤。曰。七情中不言者。爱恶欲三者。而喜哀乐生于爱。怒生于恶。喜乐由于得欲。恶哀由于不得欲。此非四之所以包七情者乎。
问。四之所以包七之义。可得闻欤。曰。七情中不言者。爱恶欲三者。而喜哀乐生于爱。怒生于恶。喜乐由于得欲。恶哀由于不得欲。此非四之所以包七情者乎。问。中和是性情之德。则何不以四端之发与未发。明性情之德。而必以七情言之也。曰。四端专是善底物。则不若以七情之兼善恶者言之也。
问。所谓未发之中者。方其静时。此心惺惺。物欲净尽。天机自露之时也。故愚蒙之意。则众人不可谓亦有未发之中矣。曰。汝言暗合于尤庵之论。然此恐不然。盖此中和。朱子以性情之德释之。则中字只当看作性。既是性则虽众人。岂无未发之中乎。语类亦有为此准备之说。可检看。
语类朱子曰。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是论圣人。只是泛论众人亦有此。与圣人都一般。或曰。恐众人未发。与圣人异否。曰。未发只做得未发。不然是无大本。道理绝了。或曰。恐众人于未发。昏了否。曰。这里未有昏明。须是还他做未发。若论原头未发都一般。只论圣人动静则全别。动亦定。静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发之中。自其感物而动。全是中节云和。众人有未发时。只是他不曾向静看。不曾知得。
问。以中为性之德。而谓众人亦有未发之中。然则禽兽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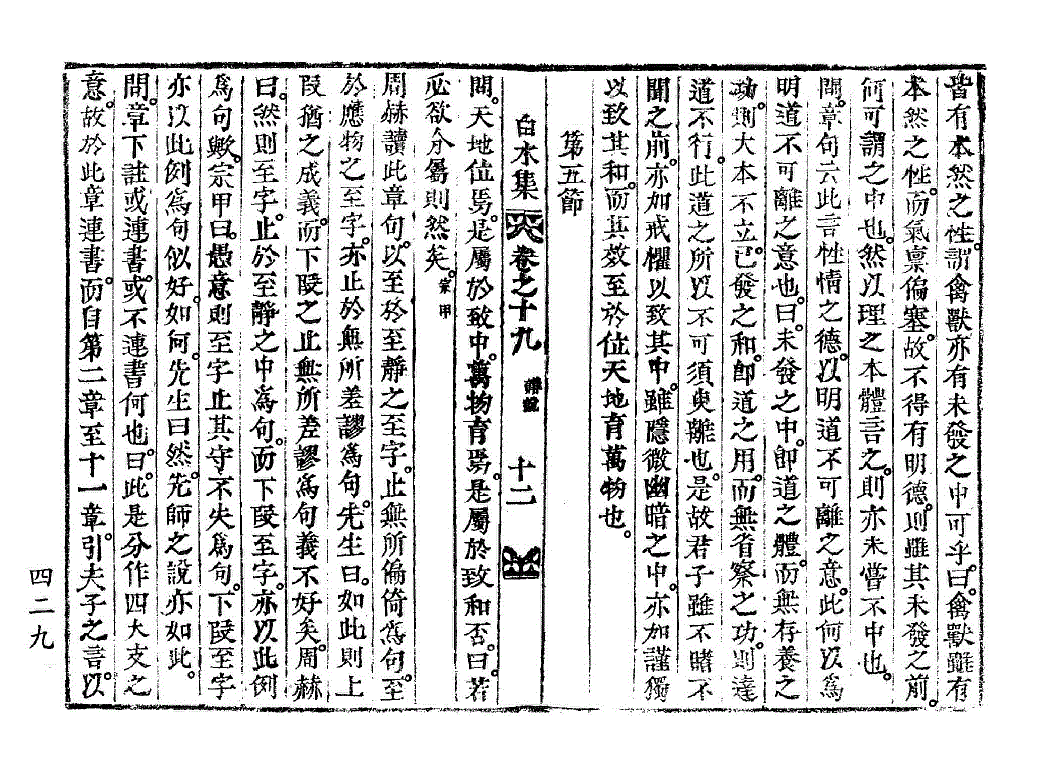 皆有本然之性。谓禽兽亦有未发之中可乎。曰。禽兽虽有本然之性。而气禀偏塞。故不得有明德。则虽其未发之前。何可谓之中也。然以理之本体言之。则亦未尝不中也。
皆有本然之性。谓禽兽亦有未发之中可乎。曰。禽兽虽有本然之性。而气禀偏塞。故不得有明德。则虽其未发之前。何可谓之中也。然以理之本体言之。则亦未尝不中也。问。章句云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此何以为明道不可离之意也。曰。未发之中。即道之体。而无存养之功。则大本不立。已发之和。即道之用。而无省察之功。则达道不行。此道之所以不可须臾离也。是故君子虽不睹不闻之前。亦加戒惧以致其中。虽隐微幽暗之中。亦加谨独以致其和。而其效至于位天地育万物也。
第五节
问。天地位焉。是属于致中。万物育焉。是属于致和否。曰。若必欲分属则然矣。(宗甲)
周赫读此章句。以至于至静之至字。止无所偏倚为句。至于应物之至字。亦止于无所差谬为句。先生曰。如此则上段犹之成义。而下段之止无所差谬为句义不好矣。周赫曰。然则至字。止于至静之中为句。而下段至字。亦以此例为句欤。宗甲曰。愚意则至字止其守不失为句。下段至字亦以此例为句似好。如何。先生曰然。先师之说亦如此。
问。章下注或连书。或不连书何也。曰。此是分作四大支之意。故于此章连书。而自第二章至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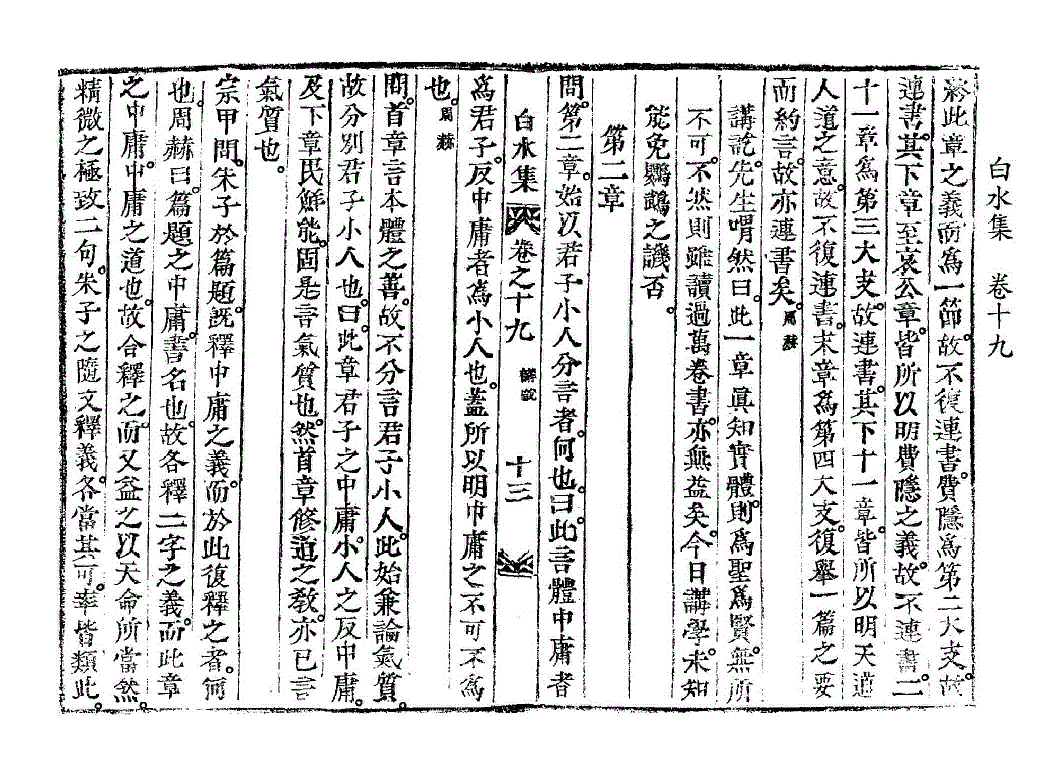 终此章之义。而为一节。故不复连书。费隐为第二大支。故连书。其下章至哀公章。皆所以明费隐之义。故不连书。二十一章为第三大支。故连书。其下十一章。皆所以明天道人道之意。故不复连书。末章为第四大支。复举一篇之要而约言。故亦连书矣。(周赫)
终此章之义。而为一节。故不复连书。费隐为第二大支。故连书。其下章至哀公章。皆所以明费隐之义。故不连书。二十一章为第三大支。故连书。其下十一章。皆所以明天道人道之意。故不复连书。末章为第四大支。复举一篇之要而约言。故亦连书矣。(周赫)讲讫。先生喟然曰。此一章真知实体。则为圣为贤。无所不可。不然则虽读过万卷书。亦无益矣。今日讲学。未知能免鹦鹉之讥否。
第二章
问。第二章。始以君子小人分言者。何也。曰。此言体中庸者为君子。反中庸者为小人也。盖所以明中庸之不可不为也。(周赫)
问。首章言本体之善。故不分言君子小人。此始兼论气质。故分别君子小人也。曰。此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及下章民鲜能。固是言气质也。然首章修道之教。亦已言气质也。
宗甲问。朱子于篇题。既释中庸之义。而于此复释之者。何也。周赫曰。篇题之中庸。书名也。故各释二字之义。而此章之中庸。中庸之道也。故合释之。而又益之以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二句。朱子之随文释义。各当其可。率皆类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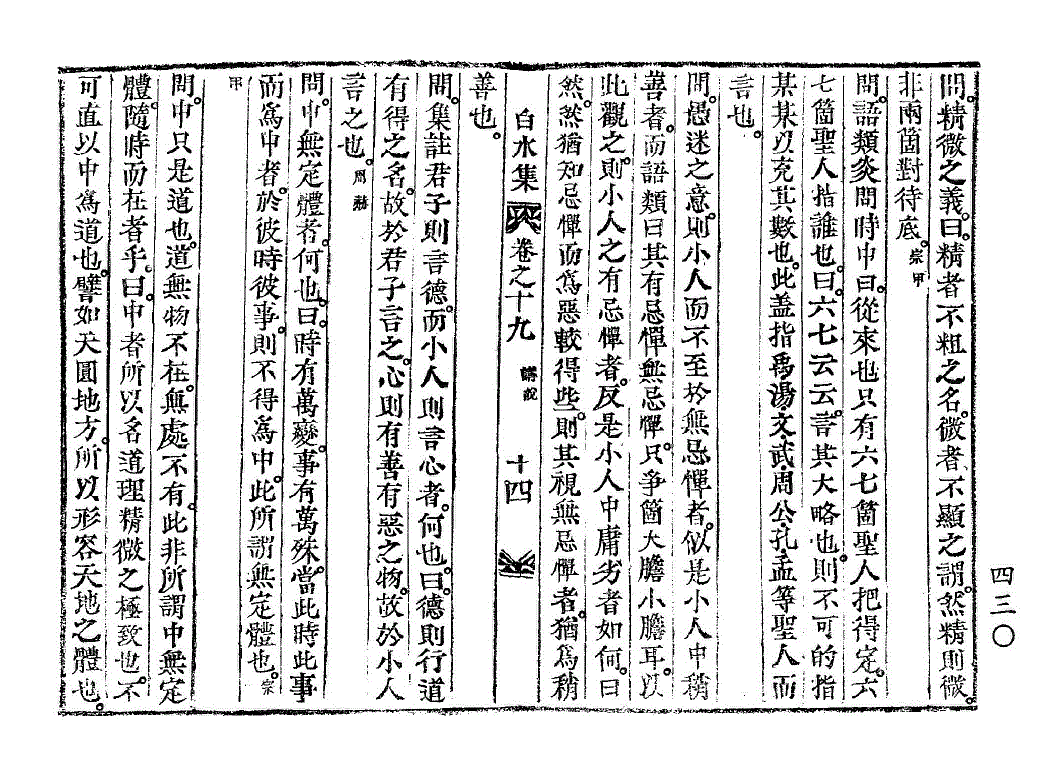 问。精微之义。曰。精者不粗之名。微者不显之谓。然精则微。非两个对待底。(宗甲)
问。精微之义。曰。精者不粗之名。微者不显之谓。然精则微。非两个对待底。(宗甲)问。语类炎问时中曰。从来也只有六七个圣人把得定。六七个圣人指谁也。曰。六七云云。言其大略也。则不可的指某某以充其数也。此盖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圣人而言也。
问。愚迷之意。则小人而不至于无忌惮者。似是小人中稍善者。而语类曰其有忌惮无忌惮。只争个大胆小胆耳。以此观之。则小人之有忌惮者。反是小人中庸劣者如何。曰然。然犹知忌惮而为恶较得些。则其视无忌惮者。犹为稍善也。
问。集注君子则言德。而小人则言心者。何也。曰。德则行道有得之名。故于君子言之。心则有善有恶之物。故于小人言之也。(周赫)
问。中无定体者。何也。曰。时有万变。事有万殊。当此时此事而为中者。于彼时彼事。则不得为中。此所谓无定体也。(宗甲)
问。中只是道也。道无物不在。无处不有。此非所谓中无定体。随时而在者乎。曰。中者所以名道理精微之极致也。不可直以中为道也。譬如天圆地方。所以形容天地之体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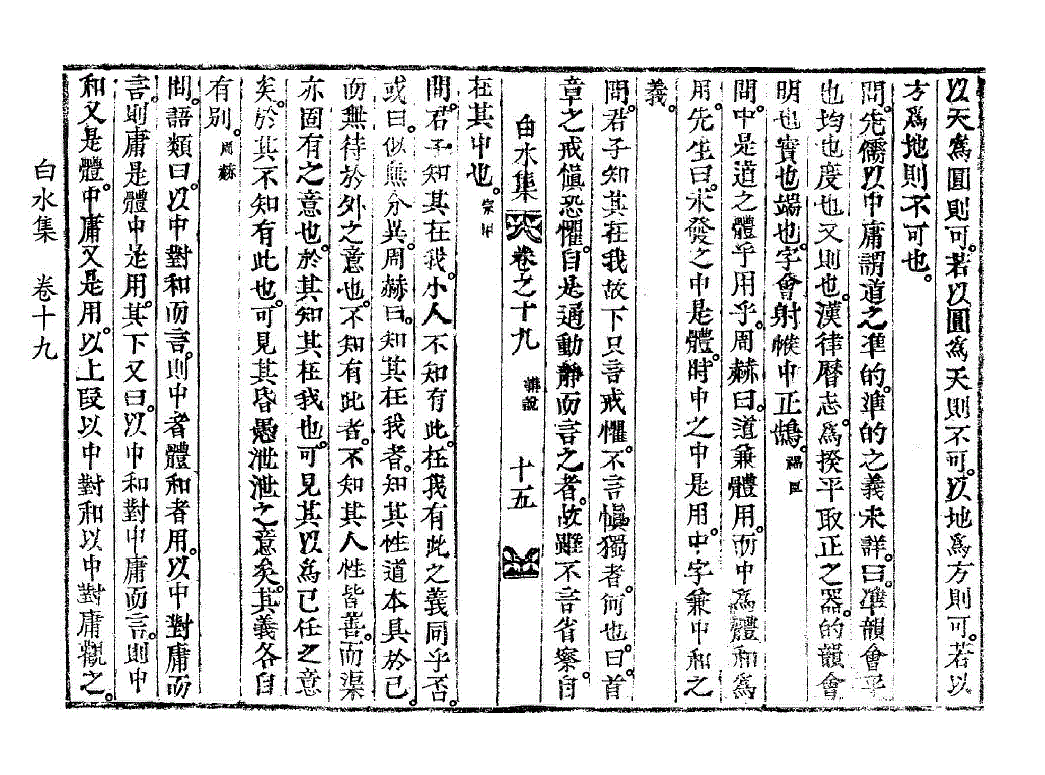 以天为圆则可。若以圆为天则不可。以地为方则可。若以方为地则不可也。
以天为圆则可。若以圆为天则不可。以地为方则可。若以方为地则不可也。问。先儒以中庸谓道之准的。准的之义未详。曰。准韵会平也均也度也又则也。汉律历志。为揆平取正之器。的韵会明也实也端也。字会射帿中正鹄。(福臣)
问。中是道之体乎用乎。周赫曰。道兼体用。而中为体和为用。先生曰。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之义。
问。君子知其在我故下只言戒惧。不言慎独者。何也。曰。首章之戒慎恐惧。自是通动静而言之者。故虽不言省察。自在其中也。(宗甲)
问。君子知其在我。小人不知有此。在我有此之义同乎否。或曰。似无分异。周赫曰。知其在我者。知其性道本具于己。而无待于外之意也。不知有此者。不知其人性皆善。而渠亦固有之意也。于其知其在我也。可见其以为己任之意矣。于其不知有此也。可见其昏愚泄泄之意矣。其义各自有别。(周赫)
问。语类曰。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以中对庸而言。则庸是体中是用。其下又曰。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以上段以中对和以中对庸观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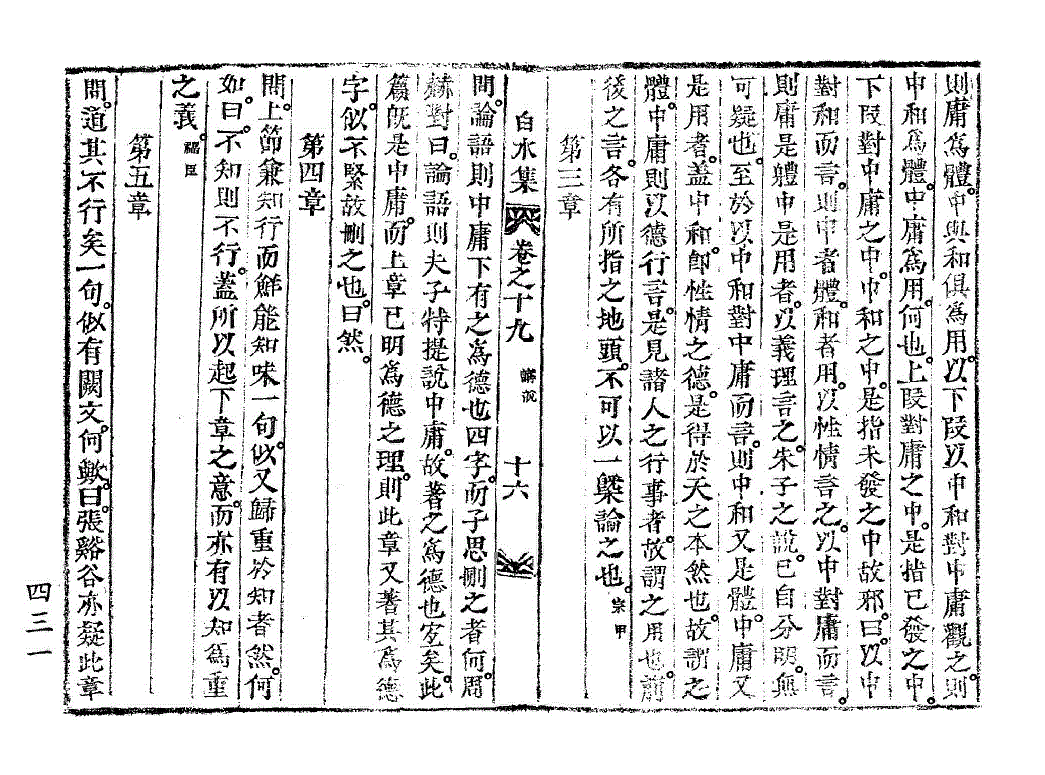 则庸为体。中与和俱为用。以下段以中和对中庸观之。则中和为体。中庸为用。何也。上段对庸之中。是指已发之中。下段对中庸之中。中和之中。是指未发之中故邪。曰。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以性情言之。以中对庸而言。则庸是体中是用者。以义理言之。朱子之说。已自分明。无可疑也。至于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者。盖中和。即性情之德。是得于天之本然也。故谓之体。中庸则以德行言。是见诸人之行事者。故谓之用也。前后之言。各有所指之地头。不可以一槩论之也。(宗甲)
则庸为体。中与和俱为用。以下段以中和对中庸观之。则中和为体。中庸为用。何也。上段对庸之中。是指已发之中。下段对中庸之中。中和之中。是指未发之中故邪。曰。以中对和而言。则中者体。和者用。以性情言之。以中对庸而言。则庸是体中是用者。以义理言之。朱子之说。已自分明。无可疑也。至于以中和对中庸而言。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者。盖中和。即性情之德。是得于天之本然也。故谓之体。中庸则以德行言。是见诸人之行事者。故谓之用也。前后之言。各有所指之地头。不可以一槩论之也。(宗甲)第三章
问。论语则中庸下有之为德也四字。而子思删之者何。周赫对曰。论语则夫子特提说中庸。故著之为德也宜矣。此篇既是中庸。而上章已明为德之理。则此章又著其为德字。似不紧故删之也。曰然。
第四章
问。上节兼知行而鲜能知味一句。似又归重于知者然。何如。曰。不知则不行。盖所以起下章之意。而亦有以知为重之义。(福臣)
第五章
问。道其不行矣一句。似有阙文。何欤。曰。张溪谷亦疑此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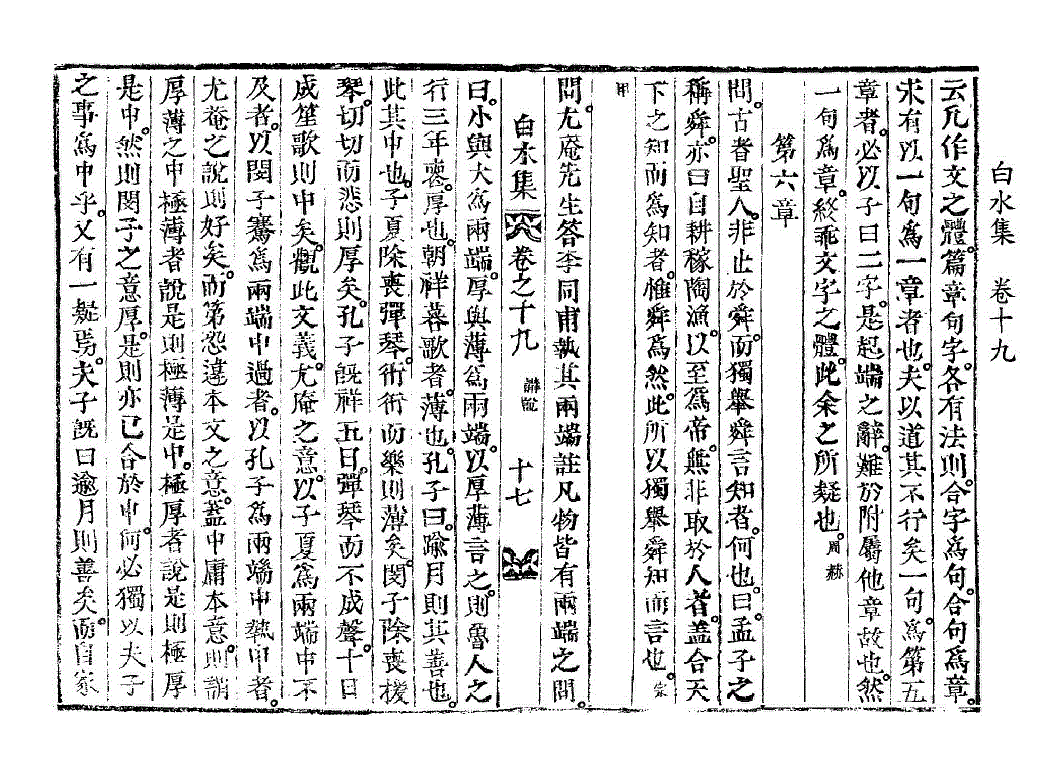 云凡作文之体。篇章句字。各有法则。合字为句。合句为章。未有以一句为一章者也。夫以道其不行矣一句。为第五章者。必以子曰二字。是起端之辞。难于附属他章故也。然一句为章。终乖文字之体。此余之所疑也。(周赫)
云凡作文之体。篇章句字。各有法则。合字为句。合句为章。未有以一句为一章者也。夫以道其不行矣一句。为第五章者。必以子曰二字。是起端之辞。难于附属他章故也。然一句为章。终乖文字之体。此余之所疑也。(周赫)第六章
问。古者圣人。非止于舜。而独举舜言知者。何也。曰。孟子之称舜。亦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盖合天下之知而为知者。惟舜为然。此所以独举舜知而言也。(宗甲)
问。尤庵先生答李同甫执其两端注凡物皆有两端之问。曰。小与大为两端。厚与薄为两端。以厚薄言之。则鲁人之行三年丧。厚也。朝祥暮歌者。薄也。孔子曰。踰月则其善也。此其中也。子夏除丧弹琴。衎衎而乐则薄矣。闵子除丧援琴。切切而悲则厚矣。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成笙歌则中矣。观此文义。尤庵之意。以子夏为两端中不及者。以闵子骞为两端中过者。以孔子为两端中执中者。尤庵之说则好矣。而第恐违本文之意。盖中庸本意。则谓厚薄之中极薄者说是则极薄是中。极厚者说是则极厚是中。然则闵子之意厚。是则亦已合于中。何必独以夫子之事为中乎。又有一疑焉。夫子既曰逾月则善矣。而自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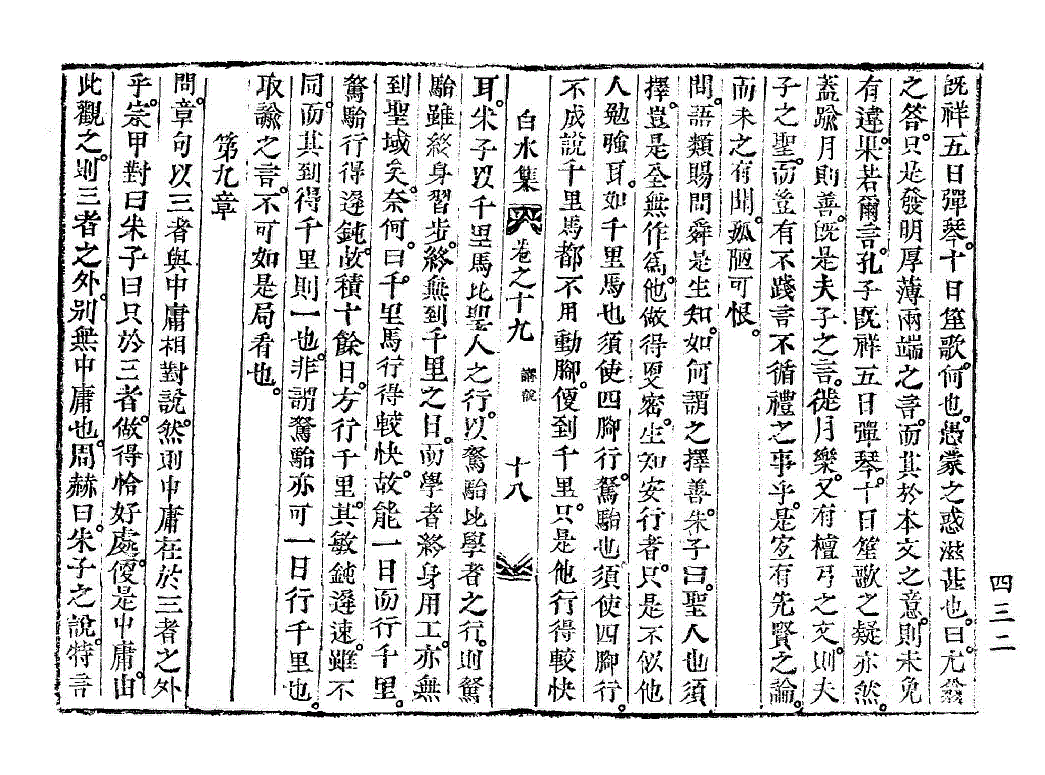 既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何也。愚蒙之惑滋甚也。曰。尤翁之答。只是发明厚薄两端之言。而其于本文之意。则未免有违。果若尔言。孔子既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之疑亦然。盖踰月则善。既是夫子之言。徙月乐。又有檀弓之文。则夫子之圣。而岂有不践言不循礼之事乎。是宜有先贤之论。而未之有闻。孤陋可恨。
既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何也。愚蒙之惑滋甚也。曰。尤翁之答。只是发明厚薄两端之言。而其于本文之意。则未免有违。果若尔言。孔子既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之疑亦然。盖踰月则善。既是夫子之言。徙月乐。又有檀弓之文。则夫子之圣。而岂有不践言不循礼之事乎。是宜有先贤之论。而未之有闻。孤陋可恨。问。语类赐问舜是生知。如何谓之择善。朱子曰。圣人也须择。岂是全无作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如千里马也须使四脚行。驽骀也。须使四脚行。不成说千里马都不用动脚。便到千里。只是他行得较快耳。朱子以千里马比圣人之行。以驽骀比学者之行。则驽骀虽终身习步。终无到千里之日。而学者终身用工。亦无到圣域矣。奈何。曰。千里马行得较快。故能一日而行千里。驽骀行得迟钝。故积十馀日。方行千里。其敏钝迟速。虽不同。而其到得千里则一也。非谓驽骀亦可一日行千里也。取谕之言。不可如是局看也。
第九章
问。章句以三者与中庸相对说。然则中庸在于三者之外乎。宗甲对曰朱子曰只于三者。做得恰好处。便是中庸。由此观之。则三者之外。别无中庸也。周赫曰。朱子之说。特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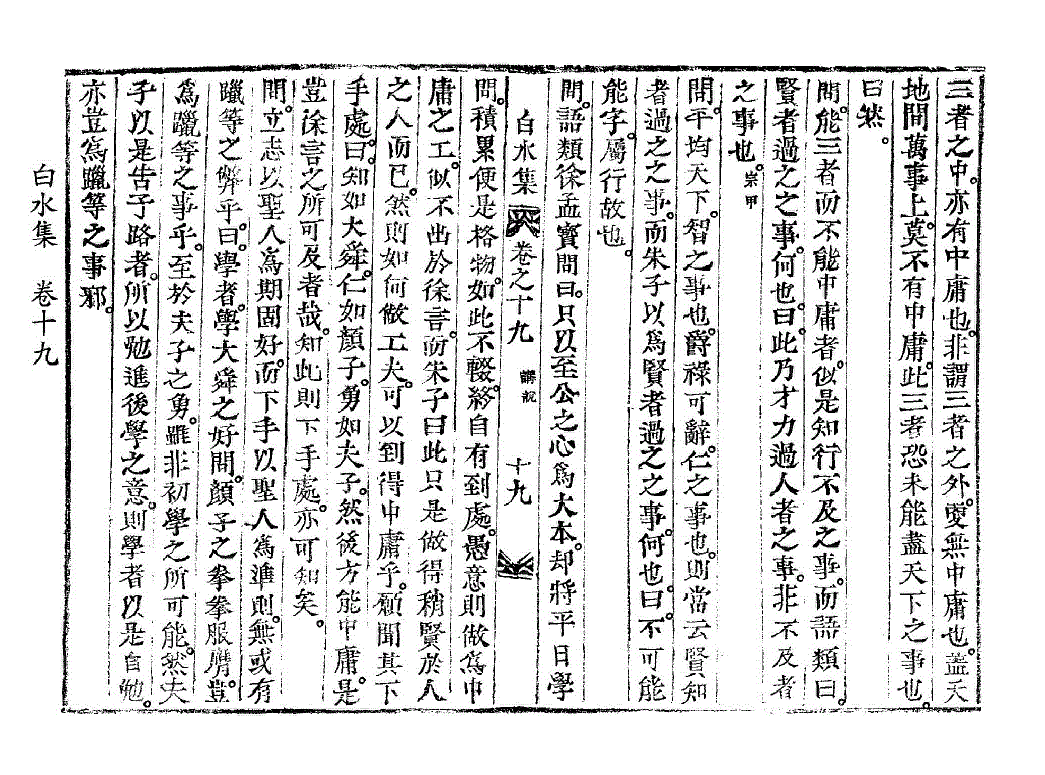 三者之中。亦有中庸也。非谓三者之外。更无中庸也。盖天地间万事上。莫不有中庸。此三者恐未能尽天下之事也。曰然。
三者之中。亦有中庸也。非谓三者之外。更无中庸也。盖天地间万事上。莫不有中庸。此三者恐未能尽天下之事也。曰然。问。能三者而不能中庸者。似是知行不及之事。而语类曰。贤者过之之事。何也。曰。此乃才力过人者之事。非不及者之事也。(宗甲)
问。平均天下。智之事也。爵禄可辞。仁之事也。则当云贤知者过之之事。而朱子以为贤者过之之事。何也。曰。不可能能字。属行故也。
问。语类徐孟宝问曰。只以至公之心为大本。却将平日学问。积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辍。终自有到处。愚意则做为中庸之工。似不出于徐言。而朱子曰此只是做得稍贤于人之人而已。然则如何做工夫。可以到得中庸乎。愿闻其下手处。曰。知如大舜。仁如颜子。勇如夫子。然后方能中庸。是岂徐言之所可及者哉。知此则下手处。亦可知矣。
问。立志以圣人为期固好。而下手以圣人为准则。无或有躐等之弊乎。曰。学者学大舜之好问。颜子之拳拳服膺。岂为躐等之事乎。至于夫子之勇。虽非初学之所可能。然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勉进后学之意。则学者以是自勉。亦岂为躐等之事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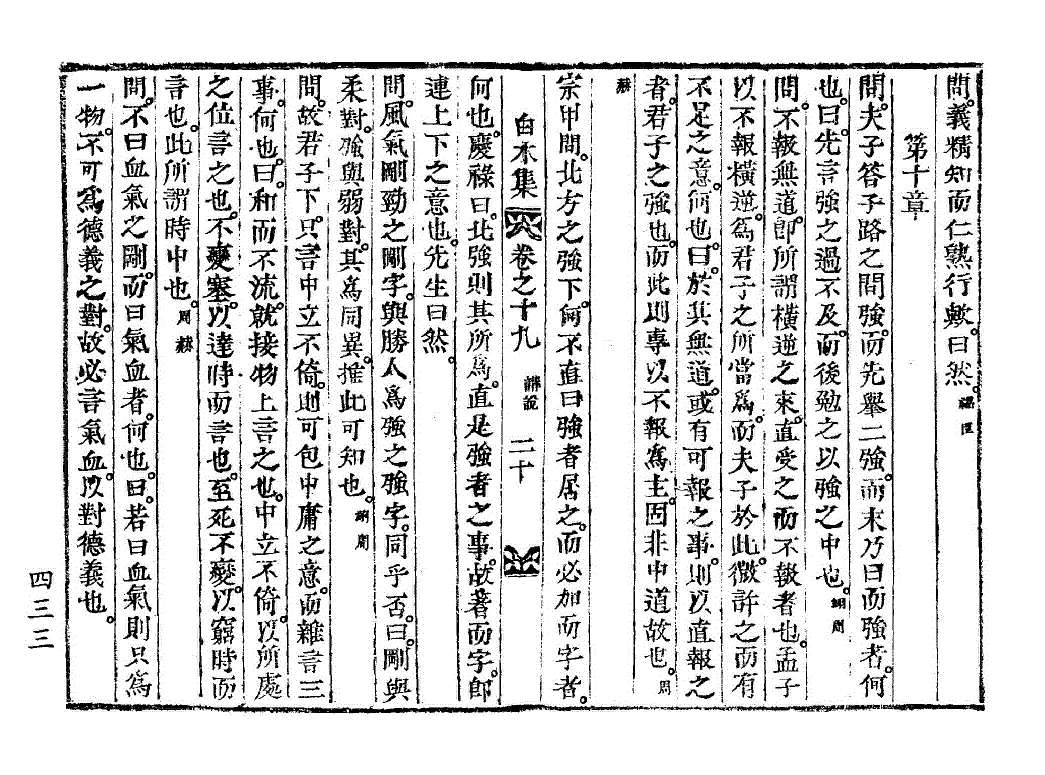 问。义精知而仁熟行欤。曰然。(福臣)
问。义精知而仁熟行欤。曰然。(福臣)第十章
问。夫子答子路之问强。而先举二强。而末乃曰而强者。何也。曰。先言强之过不及。而后勉之以强之中也。(翊周)
问。不报无道。即所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者也。孟子以不报横逆。为君子之所当为。而夫子于此。微许之而有不足之意。何也。曰。于其无道。或有可报之事。则以直报之者。君子之强也。而此则专以不报为主。固非中道故也。(周赫)
宗甲问。北方之强下。何不直曰强者居之。而必加而字者。何也。庆禄曰。北强则其所为。直是强者之事。故著而字。即连上下之意也。先生曰然。
问。风气刚劲之刚字。与胜人为强之强字。同乎否。曰。刚与柔对。强与弱对。其为同异。推此可知也。(翊周)
问。故君子下。只言中立不倚。则可包中庸之意。而杂言三事。何也。曰。和而不流。就接物上言之也。中立不倚。以所处之位言之也。不变塞。以达时而言也。至死不变。以穷时而言也。此所谓时中也。(周赫)
问。不曰血气之刚。而曰气血者。何也。曰。若曰血气则只为一物。不可为德义之对。故必言气血。以对德义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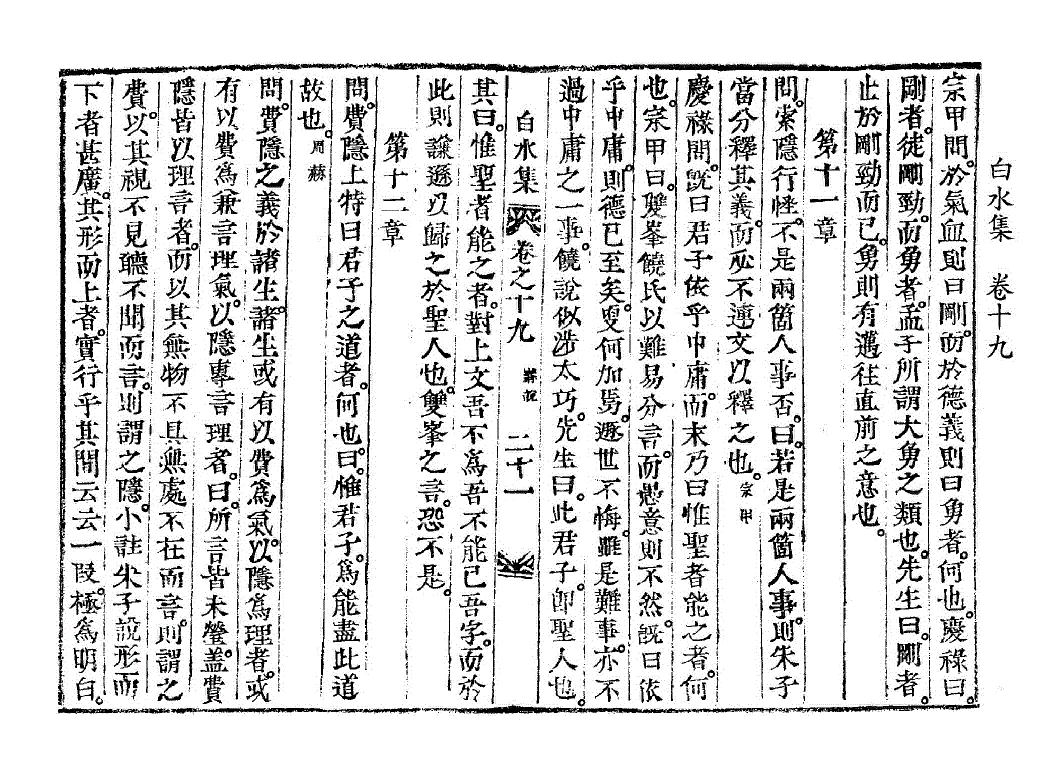 宗甲问。于气血则曰刚。而于德义则曰勇者。何也。庆禄曰。刚者。徒刚劲。而勇者。孟子所谓大勇之类也。先生曰。刚者。止于刚劲而已。勇则有迈往直前之意也。
宗甲问。于气血则曰刚。而于德义则曰勇者。何也。庆禄曰。刚者。徒刚劲。而勇者。孟子所谓大勇之类也。先生曰。刚者。止于刚劲而已。勇则有迈往直前之意也。第十一章
问。索隐行怪。不是两个人事否。曰。若是两个人事。则朱子当分释其义。而必不连文以释之也。(宗甲)
庆禄问。既曰君子依乎中庸。而末乃曰惟圣者能之者。何也。宗甲曰。双峰饶氏以难易分言。而愚意则不然。既曰依乎中庸。则德已至矣。更何加焉。遁世不悔。虽是难事。亦不过中庸之一事。饶说似涉太巧。先生曰。此君子。即圣人也。其曰。惟圣者能之者。对上文吾不为吾不能已吾字。而于此则谦逊以归之于圣人也。双峰之言。恐不是。
第十二章
问。费隐上特曰君子之道者。何也。曰。惟君子。为能尽此道故也。(周赫)
问。费隐之义于诸生。诸生或有以费为气。以隐为理者。或有以费为兼言理气。以隐专言理者。曰。所言皆未莹。盖费隐皆以理言者。而以其无物不具无处不在而言。则谓之费。以其视不见听不闻而言。则谓之隐。小注朱子说形而下者甚广。其形而上者。实行乎其间云云一段。极为明白。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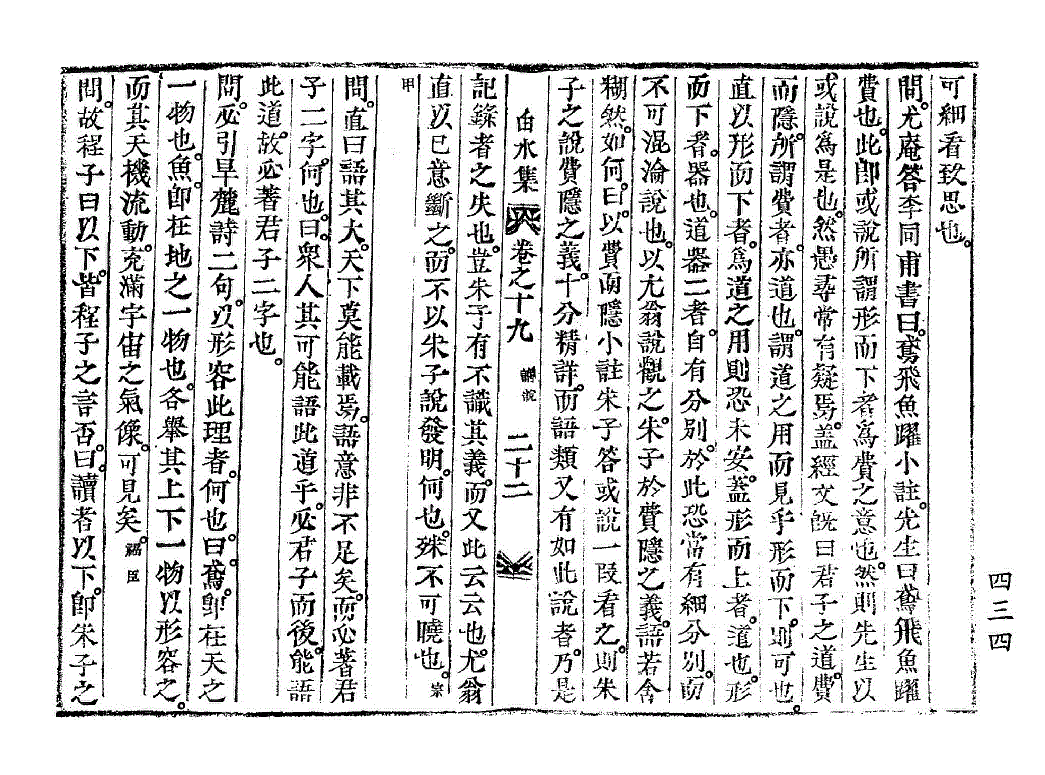 可细看致思也。
可细看致思也。问。尤庵答李同甫书曰。鸢飞鱼跃小注。先生曰鸢飞鱼跃费也。此即或说所谓形而下者为费之意也。然则先生以或说为是也。然愚寻常有疑焉。盖经文既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所谓费者。亦道也。谓道之用而见乎形而下。则可也。直以形而下者。为道之用则恐未安。盖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道器二者。自有分别。于此恐当有细分别。而不可混沦说也。以尤翁说观之。朱子于费隐之义。语若含糊然。如何。曰。以费而隐小注朱子答或说一段看之。则朱子之说费隐之义。十分精详。而语类又有如此说者。乃是记录者之失也。岂朱子有不识其义。而又此云云也。尤翁直以己意断之。而不以朱子说发明。何也。殊不可晓也。(宗甲)
问。直曰语其大。天下莫能载焉。语意非不足矣。而必著君子二字。何也。曰。众人其可能语此道乎。必君子而后。能语此道。故必著君子二字也。
问。必引旱麓诗二句。以形容此理者。何也。曰。鸢。即在天之一物也。鱼。即在地之一物也。各举其上下一物以形容之。而其天机流动。充满宇宙之气像。可见矣。(福臣)
问。故程子曰以下。皆程子之言否。曰。读者以下。即朱子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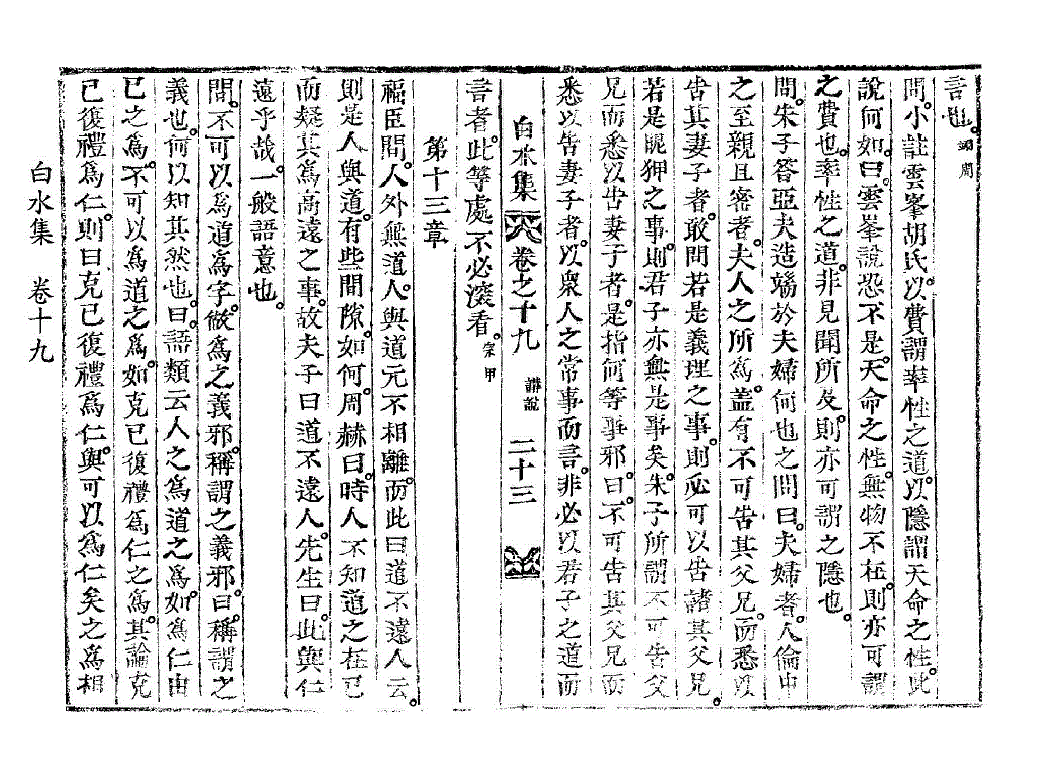 言也。(翊周)
言也。(翊周)问。小注云峰胡氏。以费谓率性之道。以隐谓天命之性。此说何如。曰。云峰说恐不是。天命之性。无物不在。则亦可谓之费也。率性之道。非见闻所及。则亦可谓之隐也。
问。朱子答亚夫造端于夫妇何也之问曰。夫妇者。人伦中之至亲且密者。夫人之所为。盖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敢问若是义理之事。则必可以告诸其父兄。若是昵狎之事。则君子亦无是事矣。朱子所谓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妻子者。是指何等事邪。曰。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妻子者。以众人之常事而言。非必以君子之道而言者。此等处不必深看。(宗甲)
第十三章
福臣问。人外无道。人与道元不相离。而此曰道不远人云。则是人与道。有些间隙。如何。周赫曰。时人不知道之在己而疑其为高远之事。故夫子曰道不远人。先生曰。此与仁远乎哉。一般语意也。
问。不可以为道为字。做为之义邪。称谓之义邪。曰。称谓之义也。何以知其然也。曰。语类云人之为道之为。如为仁由己之为。不可以为道之为。如克己复礼为仁之为。其论克己复礼为仁。则曰克己复礼为仁。与可以为仁矣之为相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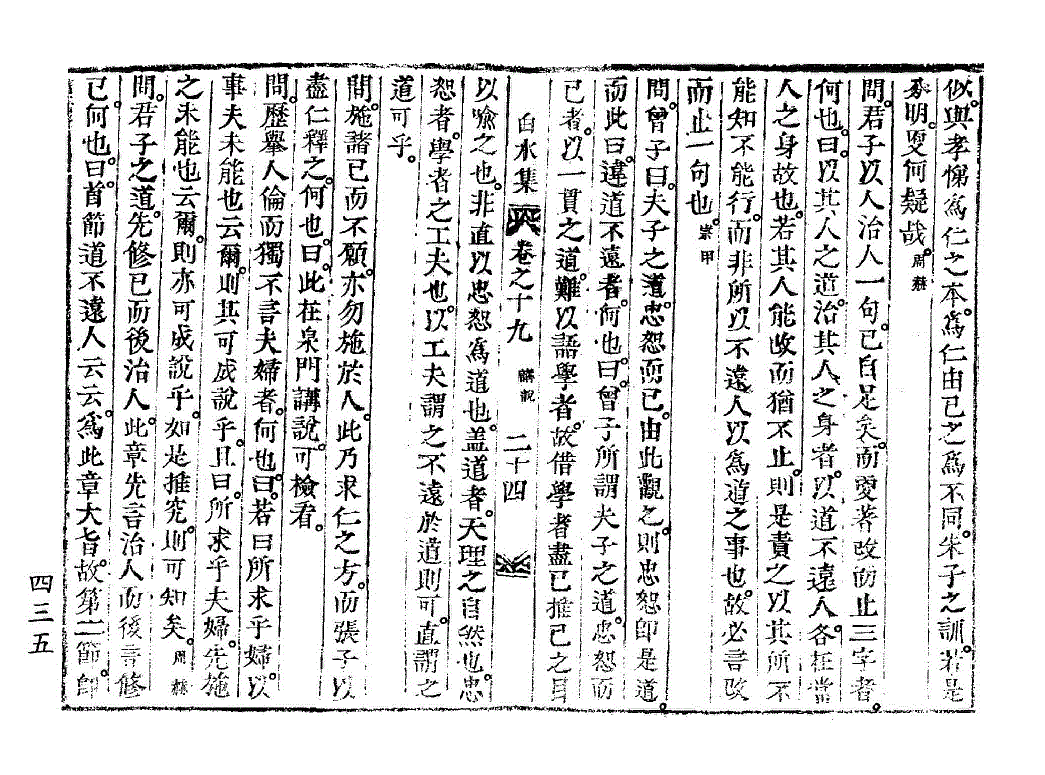 似。与孝悌为仁之本。为仁由己之为不同。朱子之训。若是分明。更何疑哉。(周赫)
似。与孝悌为仁之本。为仁由己之为不同。朱子之训。若是分明。更何疑哉。(周赫)问。君子以人治人一句。已自足矣。而更著改而止三字者。何也。曰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者。以道不远人。各在当人之身故也。若其人能改而犹不止。则是责之以其所不能知不能行。而非所以不远人以为道之事也。故必言改而止一句也。(宗甲)
问。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由此观之。则忠恕即是道。而此曰。违道不远者。何也。曰。曾子所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以一贯之道。难以语学者。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喻之也。非直以忠恕为道也。盖道者。天理之自然也。忠恕者。学者之工夫也。以工夫谓之不远于道则可。直谓之道可乎。
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乃求仁之方。而张子以尽仁释之。何也。曰。此在泉门讲说。可检看。
问。历举人伦而独不言夫妇者。何也。曰。若曰所求乎妇。以事夫未能也云尔。则其可成说乎。且曰。所求乎夫妇。先施之未能也云尔。则亦可成说乎。如是推究。则可知矣(周赫)
问。君子之道。先修己而后治人。此章先言治人而后言修己。何也。曰。首节道不远人云云。为此章大旨。故第二节。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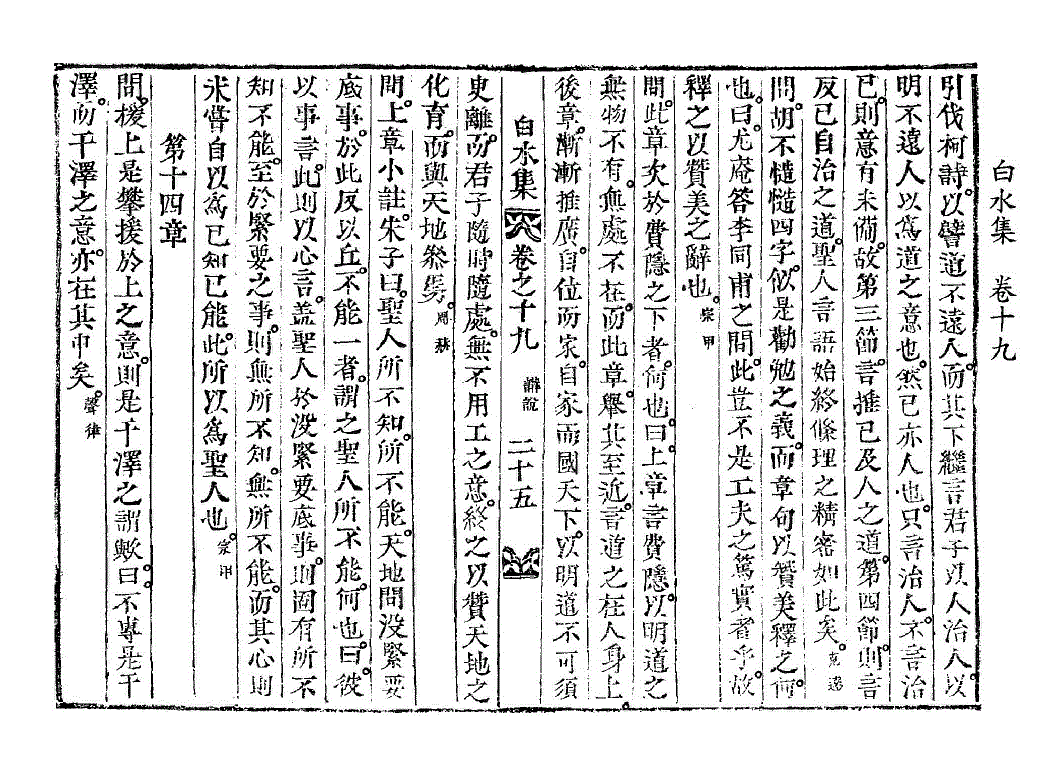 引伐柯诗。以譬道不远人。而其下继言君子以人治人。以明不远人以为道之意也。然己亦人也。只言治人。不言治己。则意有未备。故第三节。言推己及人之道。第四节。则言反己自治之道。圣人言语始终条理之精密如此矣。(克远)
引伐柯诗。以譬道不远人。而其下继言君子以人治人。以明不远人以为道之意也。然己亦人也。只言治人。不言治己。则意有未备。故第三节。言推己及人之道。第四节。则言反己自治之道。圣人言语始终条理之精密如此矣。(克远)问。胡不慥慥四字。似是劝勉之义。而章句以赞美释之。何也。曰。尤庵答李同甫之问。此岂不是工夫之笃实者乎。故释之以赞美之辞也。(宗甲)
问。此章次于费隐之下者。何也。曰。上章言费隐。以明道之无物不有。无处不在。而此章。举其至近。言道之在人身上。后章。渐渐推广。自位而家。自家而国天下。以明道不可须臾离。而君子随时随处。无不用工之意。终之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焉。(周赫)
问。上章小注。朱子曰。圣人所不知。所不能。天地间没紧要底事。于此反以丘。不能一者。谓之圣人所不能。何也。曰。彼以事言。此则以心言。盖圣人于没紧要底事。则固有所不知不能。至于紧要之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其心则未尝自以为已知已能。此所以为圣人也。(宗甲)
第十四章
问。援上是攀援于上之意。则是干泽之谓欤。曰。不专是干泽。而干泽之意。亦在其中矣。(声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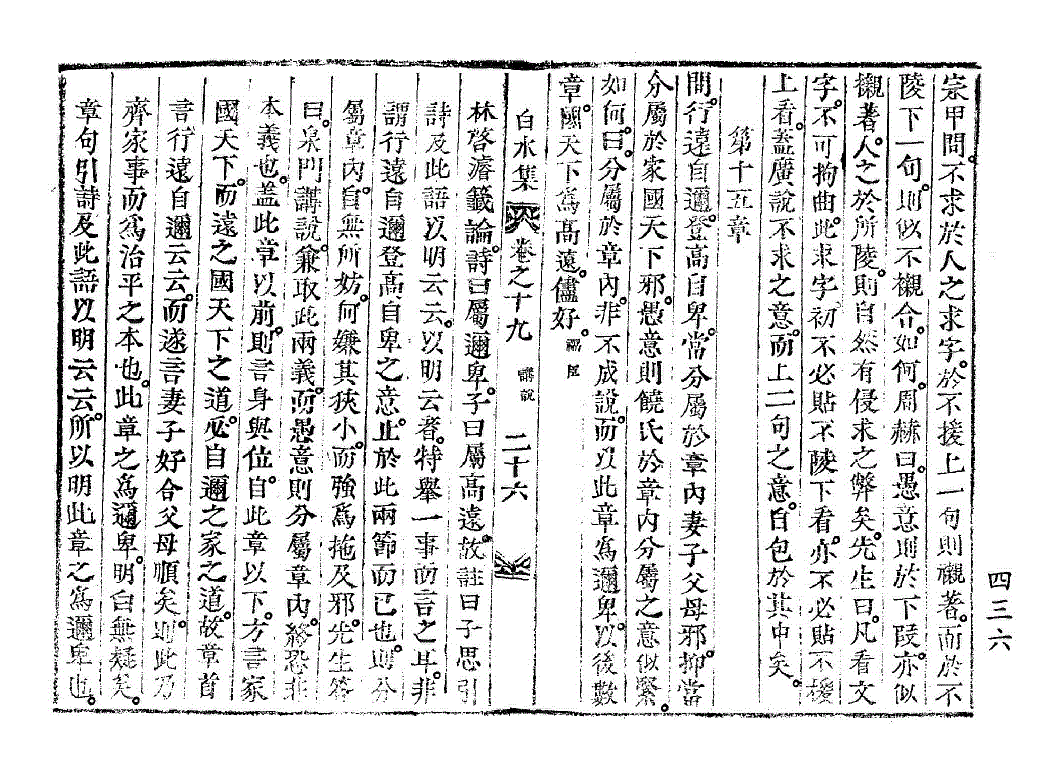 宗甲问。不求于人之求字。于不援上一句则衬著。而于不陵下一句。则似不衬合。如何。周赫曰。愚意则于下段。亦似衬著。人之于所陵。则自然有侵求之弊矣。先生曰。凡看文字。不可拘曲。此求字。初不必贴不陵下看。亦不必贴不援上看。盖广说不求之意。而上二句之意。自包于其中矣。
宗甲问。不求于人之求字。于不援上一句则衬著。而于不陵下一句。则似不衬合。如何。周赫曰。愚意则于下段。亦似衬著。人之于所陵。则自然有侵求之弊矣。先生曰。凡看文字。不可拘曲。此求字。初不必贴不陵下看。亦不必贴不援上看。盖广说不求之意。而上二句之意。自包于其中矣。第十五章
问。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当分属于章内妻子父母邪。抑当分属于家国天下邪。愚意则饶氏于章内分属之意似紧。如何。曰。分属于章内。非不成说。而以此章为迩卑。以后数章。国天下为高远。尽好。(福臣)
林启浚签论。诗曰属迩卑。子曰属高远。故注曰子思引诗及此语以明云云。以明云者。特举一事而言之耳。非谓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之意。止于此两节而已也。则分属章内。自无所妨。何嫌其狭小。而强为拖及邪。先生答曰。泉门讲说。兼取此两义。而愚意则分属章内。终恐非本义也。盖此章以前。则言身与位。自此章以下。方言家国天下。而远之国天下之道。必自迩之家之道。故章首言行远自迩云云。而遂言妻子好合父母顺矣。则此乃齐家事而为治平之本也。此章之为迩卑。明白无疑矣。章句引诗及此语以明云云。所以明此章之为迩卑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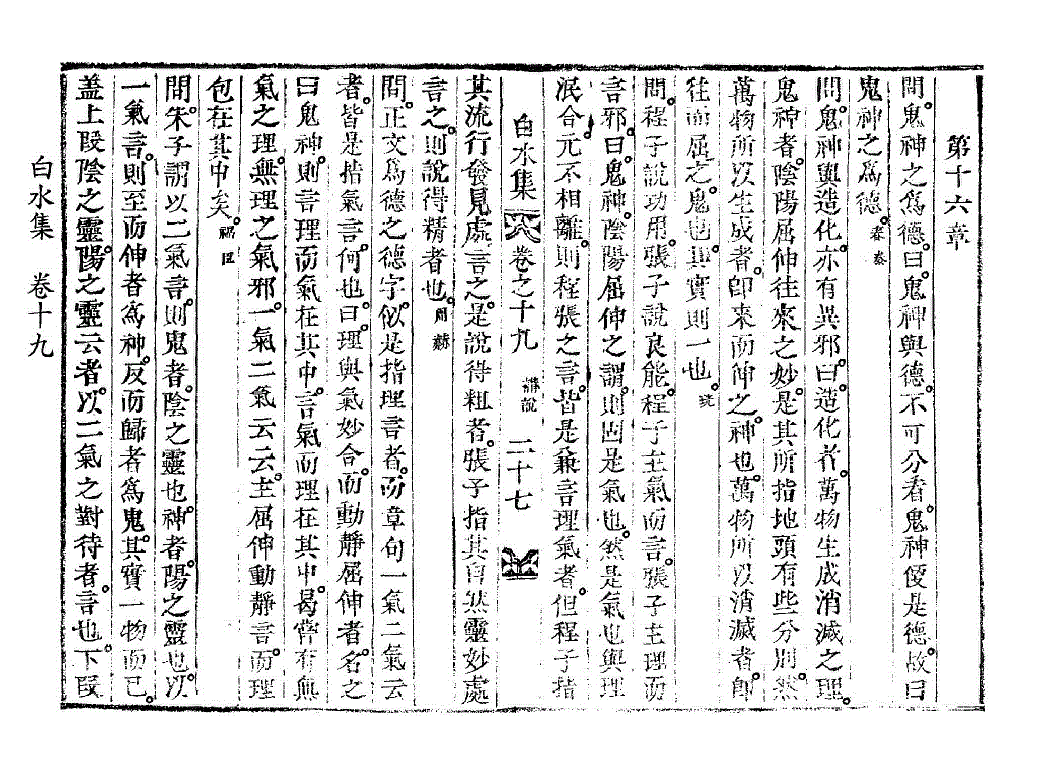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问。鬼神之为德。曰。鬼神与德。不可分看。鬼神便是德。故曰鬼神之为德。(春泰)
问。鬼神与造化。亦有异邪。曰。造化者。万物生成消灭之理。鬼神者。阴阳屈伸往来之妙。是其所指地头有些分别。然万物所以生成者。即来而伸之。神也。万物所以消灭者。即往而屈之。鬼也。其实则一也。(珖)
问。程子说功用。张子说良能。程子主气而言。张子主理而言邪。曰。鬼神。阴阳屈伸之谓。则固是气也。然是气也与理泯合。元不相离。则程张之言。皆是兼言理气者。但程子指其流行发见处言之。是说得粗者。张子指其自然灵妙处言之。则说得精者也。(周赫)
问。正文为德之德字。似是指理言者。而章句一气二气云者。皆是指气言。何也。曰。理与气妙合。而动静屈伸者。名之曰鬼神。则言理而气在其中。言气而理在其中。曷尝有无气之理。无理之气邪。一气二气云云。主屈伸动静言。而理包在其中矣。(福臣)
问。朱子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盖上段阴之灵。阳之灵云者。以二气之对待者。言也。下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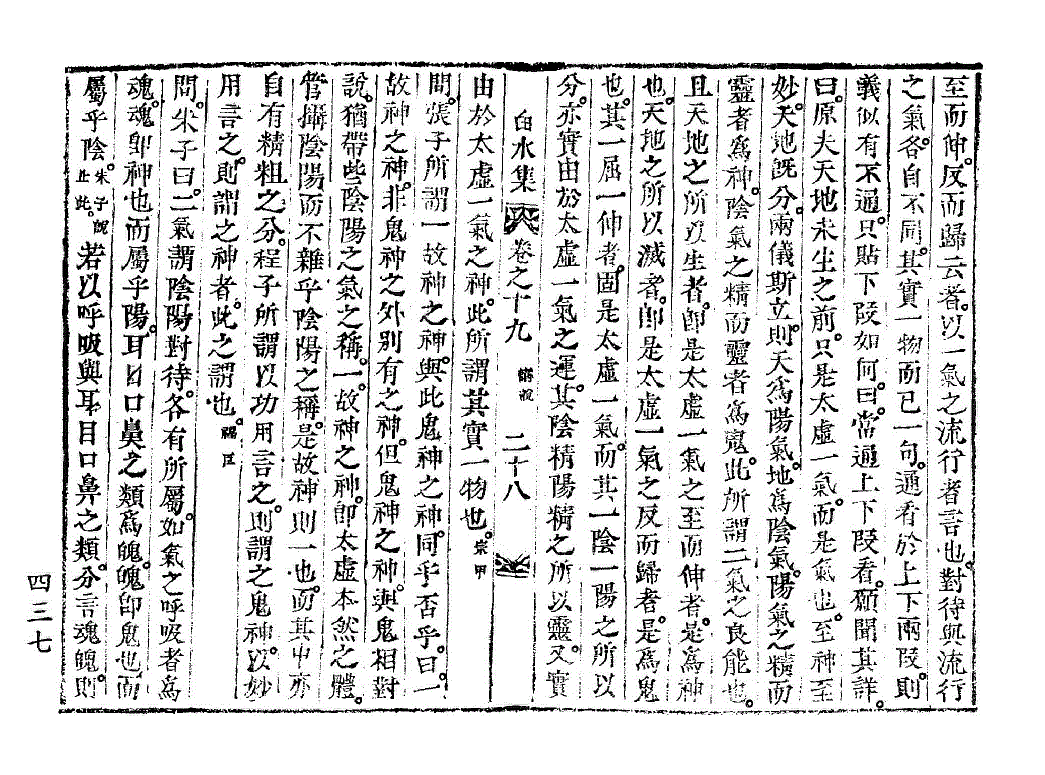 至而伸。反而归云者。以一气之流行者言也。对待与流行之气。各自不同。其实一物而已一句。通看于上下两段。则义似有不通。只贴下段如何。曰。当通上下段看。愿闻其详。曰。原夫天地未生之前。只是太虚一气。而是气也。至神至妙。天地既分。两仪斯立。则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阳气之精而灵者为神。阴气之精而灵者为鬼。此所谓二气之良能也。且天地之所以生者。即是太虚一气之至而伸者。是为神也。天地之所以灭者。即是太虚一气之反而归者。是为鬼也。其一屈一伸者。固是太虚一气。而其一阴一阳之所以分。亦实由于太虚一气之运。其阴精阳精之所以灵。又实由于太虚一气之神。此所谓其实一物也。(宗甲)
至而伸。反而归云者。以一气之流行者言也。对待与流行之气。各自不同。其实一物而已一句。通看于上下两段。则义似有不通。只贴下段如何。曰。当通上下段看。愿闻其详。曰。原夫天地未生之前。只是太虚一气。而是气也。至神至妙。天地既分。两仪斯立。则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阳气之精而灵者为神。阴气之精而灵者为鬼。此所谓二气之良能也。且天地之所以生者。即是太虚一气之至而伸者。是为神也。天地之所以灭者。即是太虚一气之反而归者。是为鬼也。其一屈一伸者。固是太虚一气。而其一阴一阳之所以分。亦实由于太虚一气之运。其阴精阳精之所以灵。又实由于太虚一气之神。此所谓其实一物也。(宗甲)问。张子所谓一故神之神。与此鬼神之神。同乎否乎。曰。一故神之神。非鬼神之外别有之神。但鬼神之神。与鬼相对说。犹带些阴阳之气之称。一。故神之神。即太虚本然之体。管摄阴阳而不杂乎阴阳之称。是故神则一也。而其中亦自有精粗之分。程子所谓以功用言之。则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则谓之神者。此之谓也。(福臣)
问。朱子曰。二气谓阴阳对待。各有所属。如气之呼吸者为魂。魂即神也而属乎阳。耳目口鼻之类为魄。魄即鬼也。而属乎阴。(朱子说止此。)若以呼吸与耳目口鼻之类。分言魂魄。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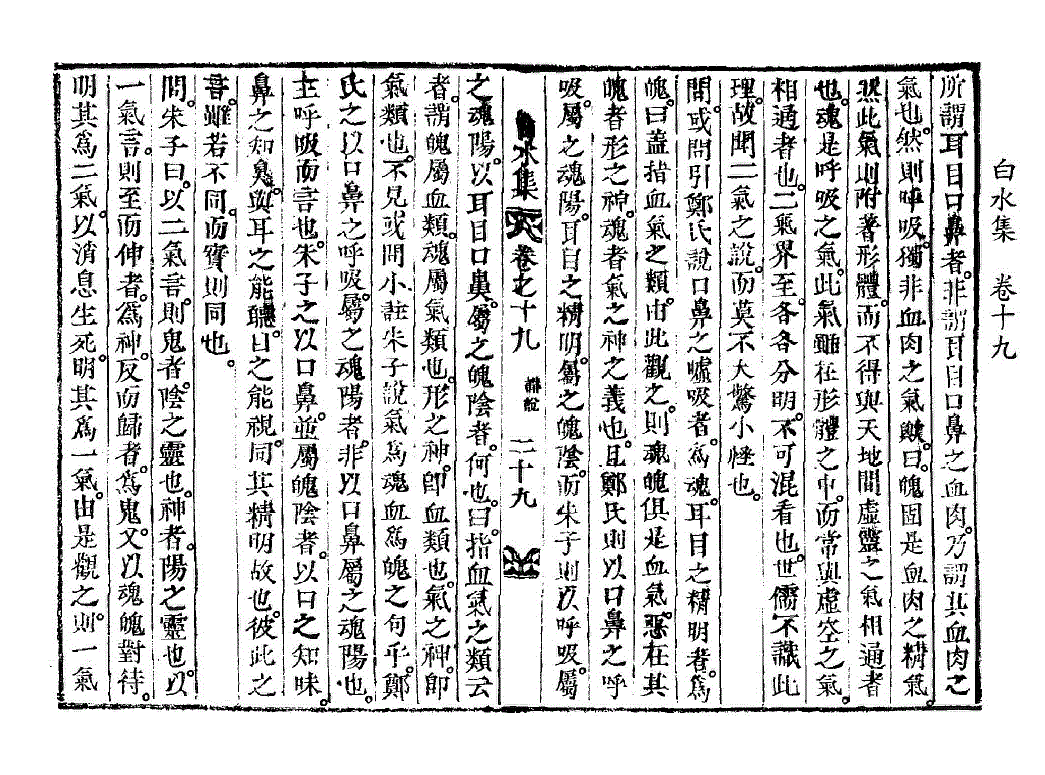 所谓耳目口鼻者。非谓耳目口鼻之血肉。乃谓其血肉之气也。然则呼吸。独非血肉之气欤。曰。魄固是血肉之精气。然此气则附著形体。而不得与天地间虚灵之气相通者也。魂是呼吸之气。此气虽在形体之中。而常与虚空之气。相通者也。二气界至。各各分明。不可混看也。世儒不识此理。故闻二气之说。而莫不大惊小怪也。
所谓耳目口鼻者。非谓耳目口鼻之血肉。乃谓其血肉之气也。然则呼吸。独非血肉之气欤。曰。魄固是血肉之精气。然此气则附著形体。而不得与天地间虚灵之气相通者也。魂是呼吸之气。此气虽在形体之中。而常与虚空之气。相通者也。二气界至。各各分明。不可混看也。世儒不识此理。故闻二气之说。而莫不大惊小怪也。问。或问引郑氏说口鼻之嘘吸者。为魂。耳目之精明者。为魄。曰盖指血气之类。由此观之。则魂魄俱是血气。恶在其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之义也。且郑氏则以口鼻之呼吸。属之魂阳。耳目之精明。属之魄阴。而朱子则以呼吸。属之魂阳。以耳目口鼻。属之魄阴者。何也。曰。指血气之类云者。谓魄属血类。魂属气类也。形之神。即血类也。气之神。即气类也。不见或问小注朱子说气为魂血为魄之句乎。郑氏之以口鼻之呼吸。属之魂阳者。非以口鼻属之魂阳也。主呼吸而言也。朱子之以口鼻。并属魄阴者。以口之知味。鼻之知臭。与耳之能听。目之能视。同其精明故也。彼此之言。虽若不同。而实则同也。
问。朱子曰。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又以魂魄对待。明其为二气。以消息生死。明其为一气。由是观之。则一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8L 页
 二气地头各异。于一气处。不可言对待。于二气处。不可言流行。而朱子释张子二气良能之义。则曰良能是说往来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又曰。屈伸往来。是二气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许多物事。一屈来便无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阴阳往来。以此段观之。则似是二气各有屈伸往来。能生死万物也。然则二气对待中。亦可言流行如何。曰。本是一气之运。而分为阴阳二气。故一气流行之中。亦有对待。二气对待之中。亦有流行。朱子之前说。言一气二气之大分也。后说言二气之中。亦各有阴阳也。
二气地头各异。于一气处。不可言对待。于二气处。不可言流行。而朱子释张子二气良能之义。则曰良能是说往来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又曰。屈伸往来。是二气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许多物事。一屈来便无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阴阳往来。以此段观之。则似是二气各有屈伸往来。能生死万物也。然则二气对待中。亦可言流行如何。曰。本是一气之运。而分为阴阳二气。故一气流行之中。亦有对待。二气对待之中。亦有流行。朱子之前说。言一气二气之大分也。后说言二气之中。亦各有阴阳也。问。流行之中。以动与静屈与伸相对说。则固为一气中对待也。对待之二气。各自屈伸往来消息生灭万物之理则未详。愿闻明教。曰。精气聚魂魄合。而生息人物。精气散魂魄离。而消灭人物。精与魄。阴也。气与魂。阳也。而其聚与合。伸也来也。其散与离。屈也往也。此非二气之各自屈伸往来消息生灭人物者乎。
问。视不见听不闻。似是专指理而言。体物不可遗。似是指气而言。然一言理一言气。则不成文理。上段则看作理气之精微。而下段则看作理气之粗迹。如何。曰。视不见。听不闻。隐也。体物而不可遗则费也。费与隐。名异而实一。何可分属气与理也。又何可分属精粗也。盖鬼神虽云气。而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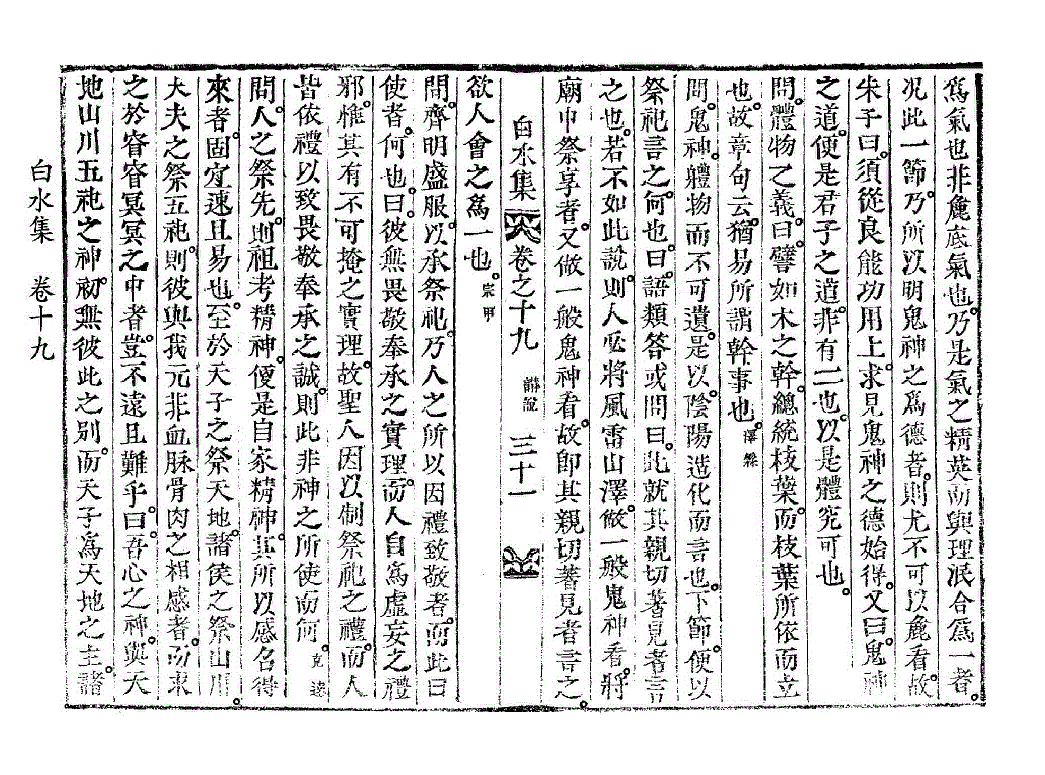 为气也非粗底气也。乃是气之精英而与理泯合为一者。况此一节。乃所以明鬼神之为德者。则尤不可以粗看。故朱子曰。须从良能功用上。求见鬼神之德始得。又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是体究可也。
为气也非粗底气也。乃是气之精英而与理泯合为一者。况此一节。乃所以明鬼神之为德者。则尤不可以粗看。故朱子曰。须从良能功用上。求见鬼神之德始得。又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以是体究可也。问。体物之义。曰。譬如木之干。总统枝叶。而枝叶所依而立也。故章句云。犹易所谓干事也。(泽霖)
问。鬼神。体物而不可遗。是以。阴阳造化而言也。下节。便以祭祀言之。何也。曰。语类答或问曰。此就其亲切著见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说。则人必将风雷山泽。做一般鬼神看。将庙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亲切著见者言之。欲人会之为一也。(宗甲)
问。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乃人之所以因礼致敬者。而此曰使者。何也。曰。彼无畏敬奉承之实理。而人自为虚妄之礼邪。惟其有不可掩之实理。故圣人因以制祭祀之礼。而人皆依礼以致畏敬奉承之诚。则此非神之所使而何。(克远)
问。人之祭先。则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其所以感召得来者。固宜速且易也。至于天子之祭天地。诸侯之祭山川。大夫之祭五祀。则彼与我元非血脉骨肉之相感者。而求之于窅窅冥冥之中者。岂不远且难乎。曰。吾心之神。与天地山川五祀之神。初无彼此之别。而天子为天地之主。诸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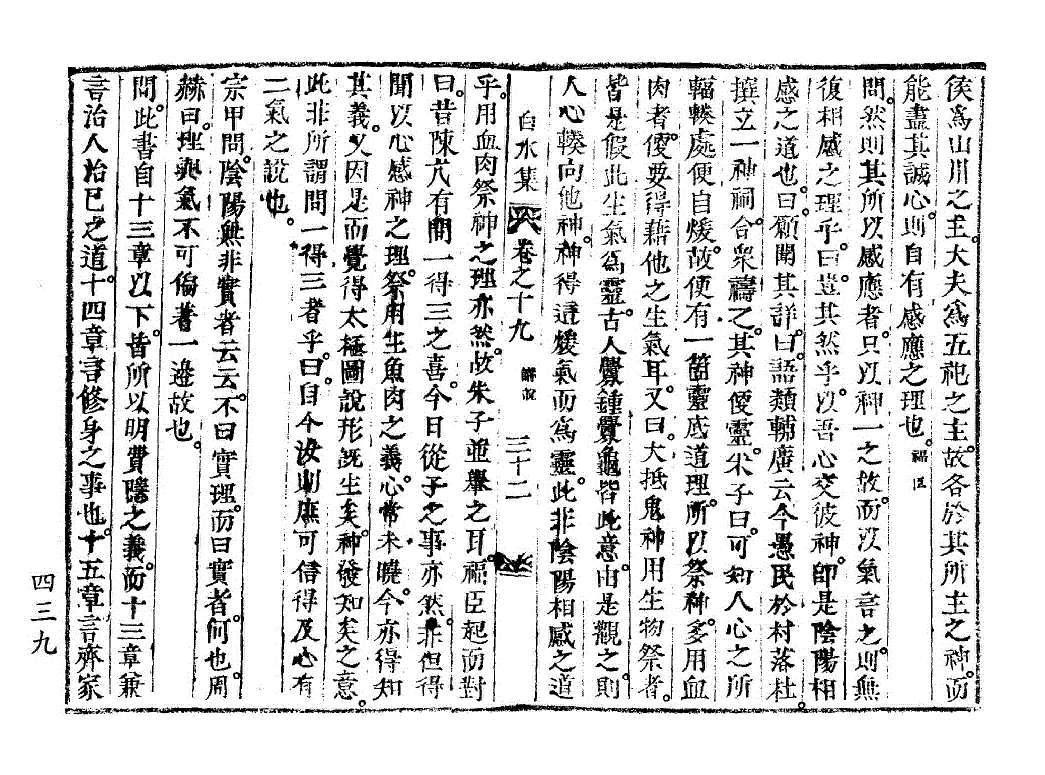 侯为山川之主。大夫为五祀之主。故各于其所主之神。而能尽其诚心。则自有感应之理也。(福臣)
侯为山川之主。大夫为五祀之主。故各于其所主之神。而能尽其诚心。则自有感应之理也。(福臣)问。然则其所以感应者。只以神一之故。而以气言之。则无复相感之理乎。曰。岂其然乎。以吾心交彼神。即是阴阳相感之道也。曰。愿闻其详。曰。语类辅广云今愚民于村落社。撰立一神祠。合众祷之。其神便灵。朱子曰。可知人心之所辐辏处便自煖。故便有一个灵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便要得藉他之生气耳。又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由是观之。则人心辏向他神。神得这煖气而为灵。此非阴阳相感之道乎。用血肉祭神之理亦然。故朱子并举之耳。福臣起而对曰。昔陈亢有问一得三之喜。今日从子之事亦然。非但得闻以心感神之理。祭用生鱼肉之义。心常未晓。今亦得知其义。又因是而觉得太极图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意。此非所谓问一得三者乎。曰。自今汝则庶可信得及心有二气之说也。
宗甲问。阴阳无非实者云云。不曰实理。而曰实者。何也。周赫曰。理与气不可偏著一边故也。
问。此书自十三章以下。皆所以明费隐之义。而十三章兼言治人治己之道。十四章。言修身之事也。十五章。言齐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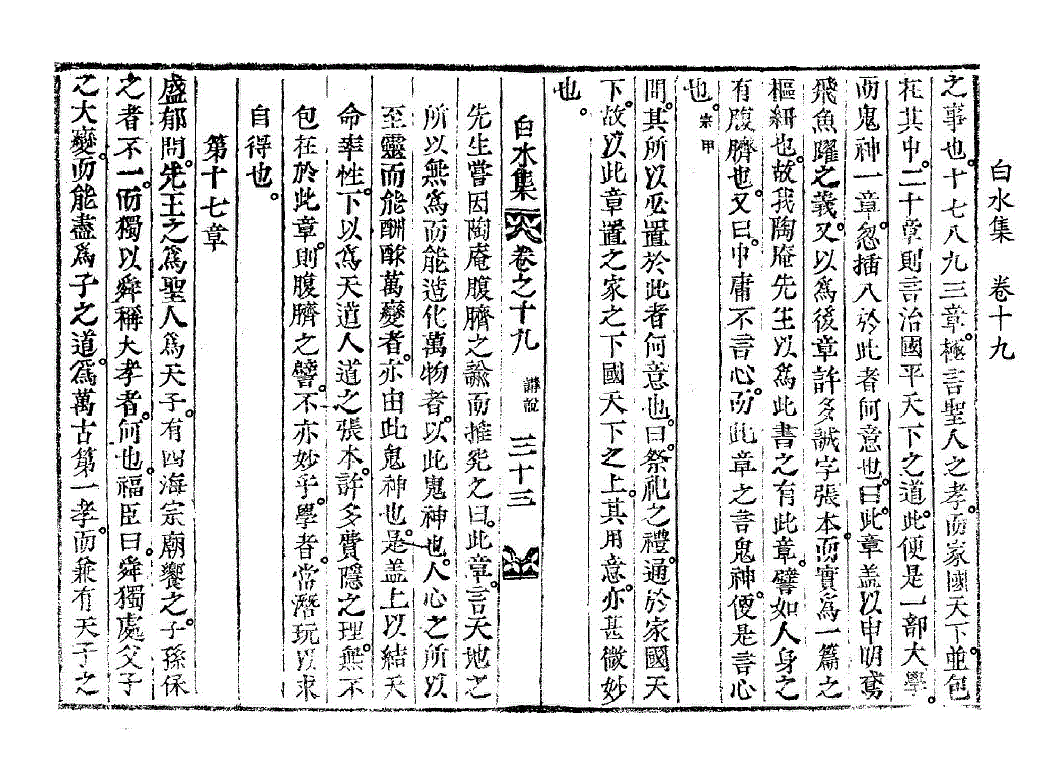 之事也。十七八九三章。极言圣人之孝。而家国天下。并包在其中。二十章则言治国平天下之道。此便是一部大学。而鬼神一章。忽插入于此者何意也。曰。此章盖以申明鸢飞鱼跃之义。又以为后章许多诚字张本。而实为一篇之枢纽也。故我陶庵先生以为此书之有此章。譬如人身之有腹脐也。又曰。中庸不言心。而此章之言鬼神。便是言心也。(宗甲)
之事也。十七八九三章。极言圣人之孝。而家国天下。并包在其中。二十章则言治国平天下之道。此便是一部大学。而鬼神一章。忽插入于此者何意也。曰。此章盖以申明鸢飞鱼跃之义。又以为后章许多诚字张本。而实为一篇之枢纽也。故我陶庵先生以为此书之有此章。譬如人身之有腹脐也。又曰。中庸不言心。而此章之言鬼神。便是言心也。(宗甲)问。其所以必置于此者何意也。曰。祭祀之礼。通于家国天下。故以此章置之家之下国天下之上。其用意。亦甚微妙也。
先生尝因陶庵腹脐之谕而推究之曰。此章。言天地之所以无为而能造化万物者。以此鬼神也。人心之所以至灵而能酬酢万变者。亦由此鬼神也。是盖上以结天命率性。下以为天道人道之张本。许多费隐之理。无不包在于此章。则腹脐之譬。不亦妙乎。学者。当潜玩以求自得也。
第十七章
盛郁问。先王之为圣人为天子。有四海宗庙飨之。子孙保之者不一。而独以舜称大孝者。何也。福臣曰。舜独处父子之大变。而能尽为子之道。为万古第一孝。而兼有天子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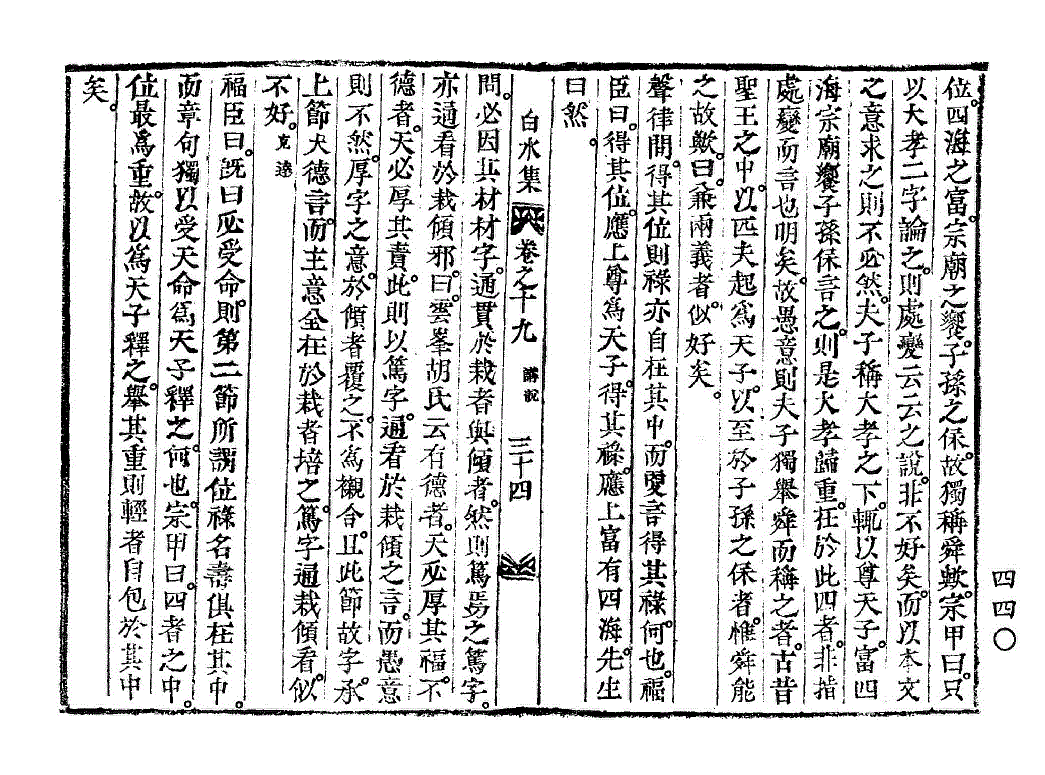 位。四海之富。宗庙之飨。子孙之保。故独称舜欤。宗甲曰。只以大孝二字论之。则处变云云之说。非不好矣。而以本文之意求之则不必然。夫子称大孝之下。辄以尊天子。富四海宗庙飨子孙保言之。则是大孝归重。在于此四者。非指处变而言也明矣。故愚意则夫子独举舜而称之者。古昔圣王之中。以匹夫起为天子。以至于子孙之保者。惟舜能之故欤。曰。兼两义者。似好矣。
位。四海之富。宗庙之飨。子孙之保。故独称舜欤。宗甲曰。只以大孝二字论之。则处变云云之说。非不好矣。而以本文之意求之则不必然。夫子称大孝之下。辄以尊天子。富四海宗庙飨子孙保言之。则是大孝归重。在于此四者。非指处变而言也明矣。故愚意则夫子独举舜而称之者。古昔圣王之中。以匹夫起为天子。以至于子孙之保者。惟舜能之故欤。曰。兼两义者。似好矣。声律问。得其位则禄亦自在其中。而更言得其禄。何也。福臣曰。得其位。应上尊为天子。得其禄。应上富有四海。先生曰然。
问。必因其材材字。通贯于栽者与倾者。然则笃焉之笃字。亦通看于栽倾邪。曰。云峰胡氏云有德者。天必厚其福。不德者。天必厚其责。此则以笃字。通看于栽倾之言。而愚意则不然。厚字之意。于倾者覆之。不为衬合。且此节故字。承上节大德言。而主意全在于栽者培之。笃字通栽倾看。似不好。(克远)
福臣曰。既曰必受命。则第二节所谓位禄名寿俱在其中。而章句独以受天命为天子释之。何也。宗甲曰。四者之中。位最为重。故以为天子释之。举其重则轻者自包于其中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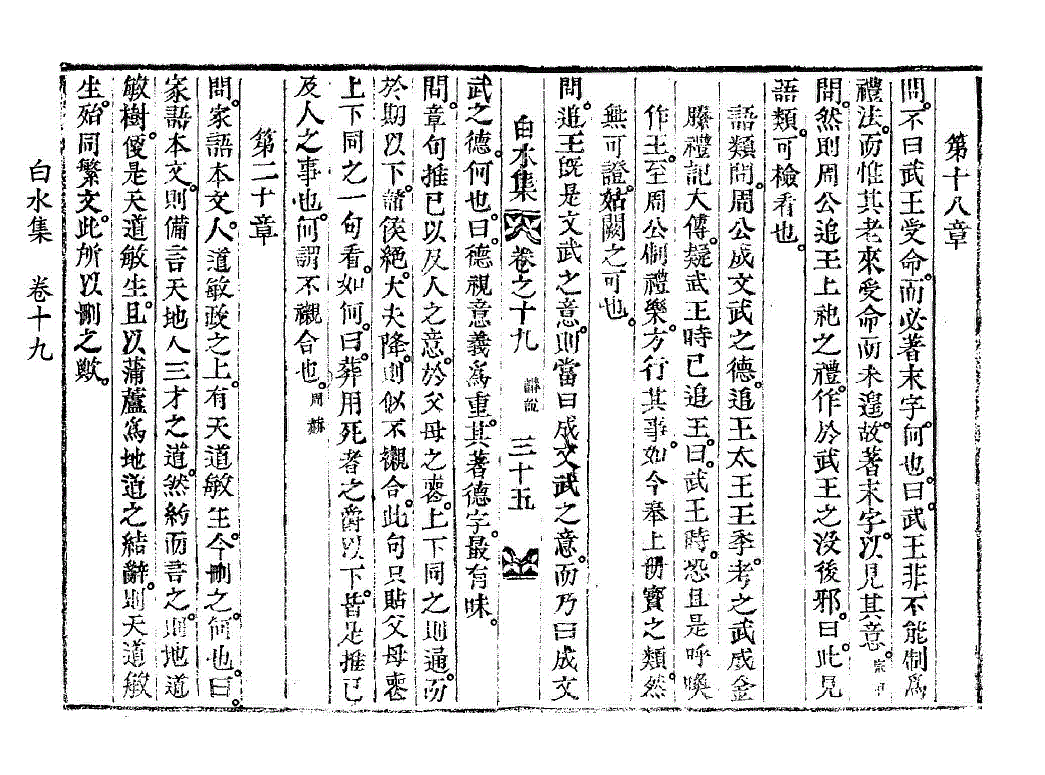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问。不曰武王受命。而必著末字。何也。曰。武王非不能制为礼法。而惟其老来受命而未遑。故著末字。以见其意。(宗甲)
问。然则周公追王上祀之礼。作于武王之没后邪。曰。此见语类。可检看也。
语类问。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礼记大传。疑武王时已追王。曰。武王时。恐且是呼唤作王。至周公制礼乐。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宝之类。然无可證。姑阙之可也。
问。追王既是文武之意。则当曰成文武之意。而乃曰成文武之德。何也。曰。德视意义为重。其著德字。最有味。
问。章句推己以及人之意。于父母之丧。上下同之则通。而于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则似不衬合。此句只贴父母丧上下同之一句看。如何。曰。葬用死者之爵以下。皆是推己及人之事也。何谓不衬合也。(周赫)
第二十章
问。家语本文。人道敏政之上。有天道敏生。今删之。何也。曰。家语本文。则备言天地人三才之道。然约而言之。则地道敏树。便是天道敏生。且以蒲芦为地道之结辞。则天道敏生。殆同繁文。此所以删之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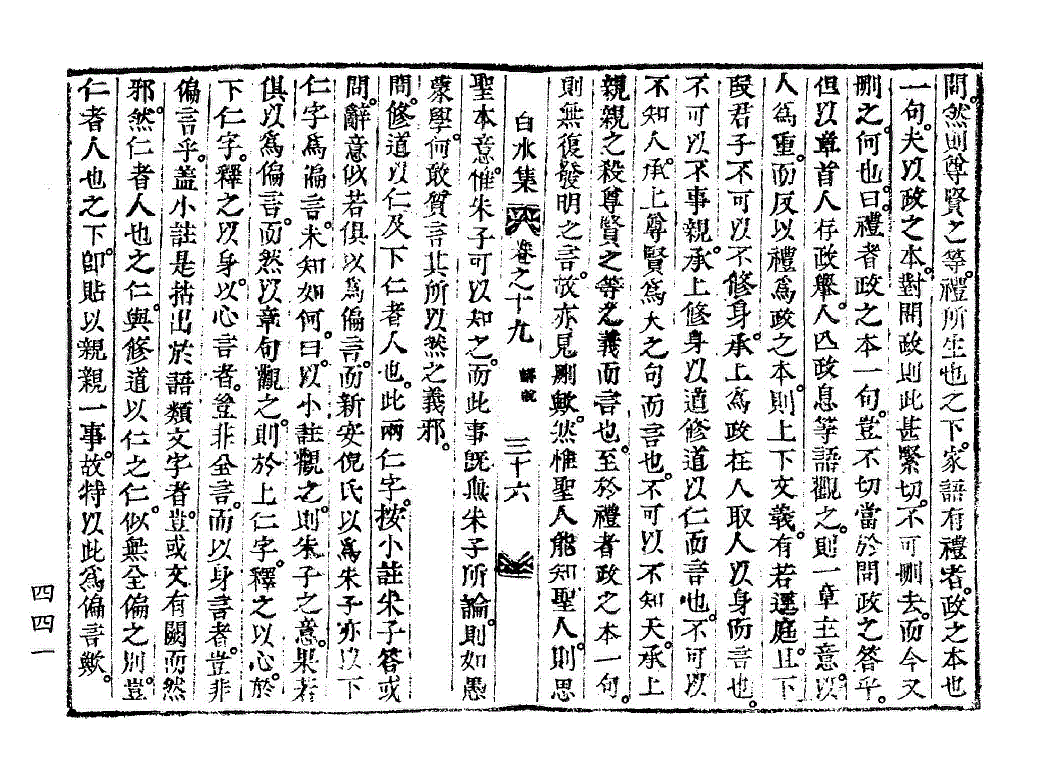 问。然则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之下。家语有礼者。政之本也一句。夫以政之本。对问政则此甚紧切。不可删去。而今又删之。何也。曰。礼者政之本一句。岂不切当于问政之答乎。但以章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等语观之。则一章主意。以人为重。而反以礼为政之本。则上下文义。有若径庭。且下段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承上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而言也。不可以不事亲。承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言也。不可以不知人。承上尊贤为大之句而言也。不可以不知天。承上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之义而言也。至于礼者政之本一句。则无复发明之言。故亦见删欤。然惟圣人能知圣人。则思圣本意。惟朱子可以知之。而此事既无朱子所论。则如愚蒙学。何敢质言其所以然之义邪。
问。然则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之下。家语有礼者。政之本也一句。夫以政之本。对问政则此甚紧切。不可删去。而今又删之。何也。曰。礼者政之本一句。岂不切当于问政之答乎。但以章首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等语观之。则一章主意。以人为重。而反以礼为政之本。则上下文义。有若径庭。且下段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承上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而言也。不可以不事亲。承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而言也。不可以不知人。承上尊贤为大之句而言也。不可以不知天。承上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之义而言也。至于礼者政之本一句。则无复发明之言。故亦见删欤。然惟圣人能知圣人。则思圣本意。惟朱子可以知之。而此事既无朱子所论。则如愚蒙学。何敢质言其所以然之义邪。问。修道以仁及下仁者人也。此两仁字。按小注朱子答或问。辞意似若俱以为偏言。而新安倪氏以为朱子亦以下仁字为偏言。未知如何。曰。以小注观之。则朱子之意。果若俱以为偏言。而然以章句观之。则于上仁字。释之以心。于下仁字。释之以身。以心言者。岂非全言。而以身言者。岂非偏言乎。盖小注是拈出于语类文字者。岂或文有阙而然邪。然仁者人也之仁。与修道以仁之仁。似无全偏之别。岂仁者人也之下。即贴以亲亲一事。故特以此为偏言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2H 页
 问。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所生也。但举五性之三而不言智信者。何也。曰。此非所以明性理之言。则其于五性。何必一一言之。而通下文观之。则知人知天。其非知也邪。曰。一曰诚。其非信也邪。
问。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礼所生也。但举五性之三而不言智信者。何也。曰。此非所以明性理之言。则其于五性。何必一一言之。而通下文观之。则知人知天。其非知也邪。曰。一曰诚。其非信也邪。问。天下之达道。此达道。与首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之达同欤。曰。首章。以情言。此。以五伦言。首章。性之发于情者。此。性之见于行者。所言。各有地头。
问。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既诚字之意也。则何不直曰诚也。而必曰一也邪。曰。达道有五。达德有三。皆不一也。而所以行之者。则只是一诚而已。故著一字以作三五之对。则语意尤为有味也。
问。吕氏说企生知安行之资。轻困知勉行云云。困知勉行。亦是资也。而不言资者。何也。曰。凡人之见贤而企之者。必归之于资品之美。见不贤而轻之者。不暇归之于资品之不美。而辄诮其不能下字甚当。
问。力行与勉行。何以有差等。而勉行则为三德。力行则为三近邪。曰。勉行与力行。无差等之可言。而勉行之勉字。与安行之安利行之利为对语。故入于三德之列也。力行之力字。则非安与利之对。而力行二字。与好学为对。此所以不入于三德而归于三近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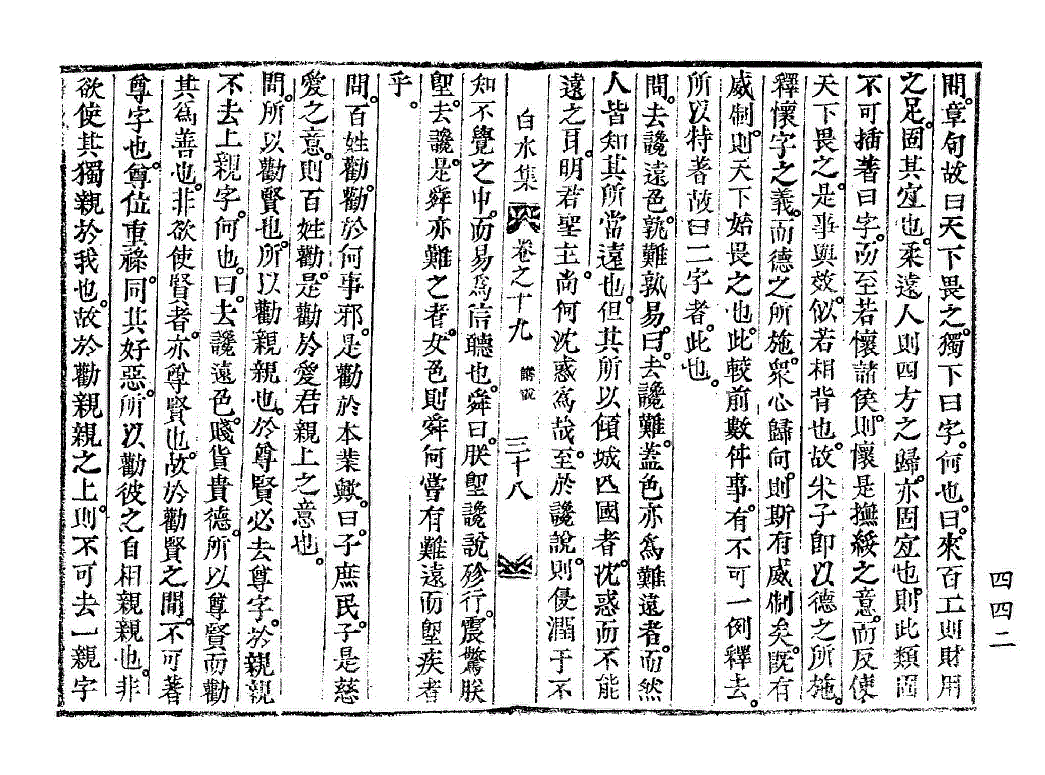 问。章句故曰天下畏之。独下曰字。何也。曰。来百工则财用之足。固其宜也。柔远人则四方之归。亦固宜也。则此类固不可插著曰字。而至若怀诸侯。则怀是抚绥之意。而反使天下畏之。是事与效。似若相背也。故朱子即以德之所施。释怀字之义。而德之所施。众心归向。则斯有威制矣。既有威制。则天下始畏之也。此较前数件事。有不可一例释去。所以特著故曰二字者。此也。
问。章句故曰天下畏之。独下曰字。何也。曰。来百工则财用之足。固其宜也。柔远人则四方之归。亦固宜也。则此类固不可插著曰字。而至若怀诸侯。则怀是抚绥之意。而反使天下畏之。是事与效。似若相背也。故朱子即以德之所施。释怀字之义。而德之所施。众心归向。则斯有威制矣。既有威制。则天下始畏之也。此较前数件事。有不可一例释去。所以特著故曰二字者。此也。问。去谗远色。孰难孰易。曰。去谗难。盖色亦为难远者。而然人皆知其所当远也。但其所以倾城亡国者。沈惑而不能远之耳。明君圣主。尚何沈惑为哉。至于谗说。则侵润于不知不觉之中。而易为信听也。舜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堲。去谗。是舜亦难之者。女色则舜何尝有难远而堲疾者乎。
问。百姓劝。劝于何事邪。是劝于本业欤。曰。子庶民。子是慈爱之意。则百姓劝。是劝于爱君亲上之意也。
问。所以劝贤也。所以劝亲亲也。于尊贤必去尊字。于亲亲不去上亲字。何也。曰。去谗远色。贱货贵德。所以尊贤而劝其为善也。非欲使贤者。亦尊贤也。故于劝贤之间。不可著尊字也。尊位重禄。同其好恶。所以劝彼之自相亲亲也。非欲使其独亲于我也。故于劝亲亲之上。则不可去一亲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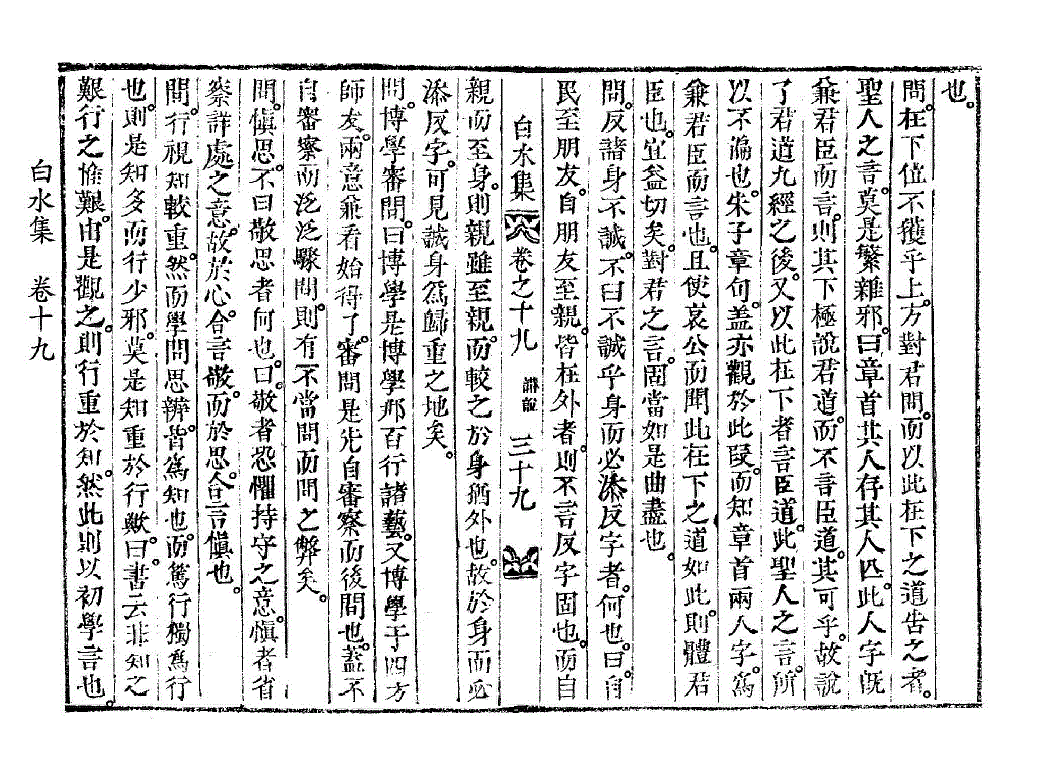 也。
也。问。在下位不获乎上。方对君问。而以此在下之道告之者。圣人之言。莫是繁杂邪。曰章首其人存其人亡。此人字既兼君臣而言。则其下极说君道。而不言臣道。其可乎。故说了君道九经之后。又以此在下者言臣道。此圣人之言。所以不偏也。朱子章句。盖亦观于此段。而知章首两人字。为兼君臣而言也。且使哀公而闻此在下之道如此。则体君臣也。宜益切矣。对君之言。固当如是曲尽也。
问。反诸身不诚。不曰不诚乎身而必添反字者。何也。曰。自民至朋友。自朋友至亲。皆在外者。则不言反字固也。而自亲而至身。则亲虽至亲。而较之于身犹外也。故于身而必添反字。可见诚身为归重之地矣。
问。博学审问。曰博学是博学那百行诸艺。又博学于四方师友。两意兼看始得了。审问是先自审察而后问也。盖不自审察而泛泛骤问。则有不当问而问之弊矣。
问。慎思。不曰敬思者何也。曰。敬者恐惧持守之意。慎者省察详处之意。故于心。合言敬。而于思。合言慎也。
问。行视知较重。然而学问思辨。皆为知也。而笃行独为行也。则是知多而行少邪。莫是知重于行欤。曰。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由是观之。则行重于知。然此则以初学言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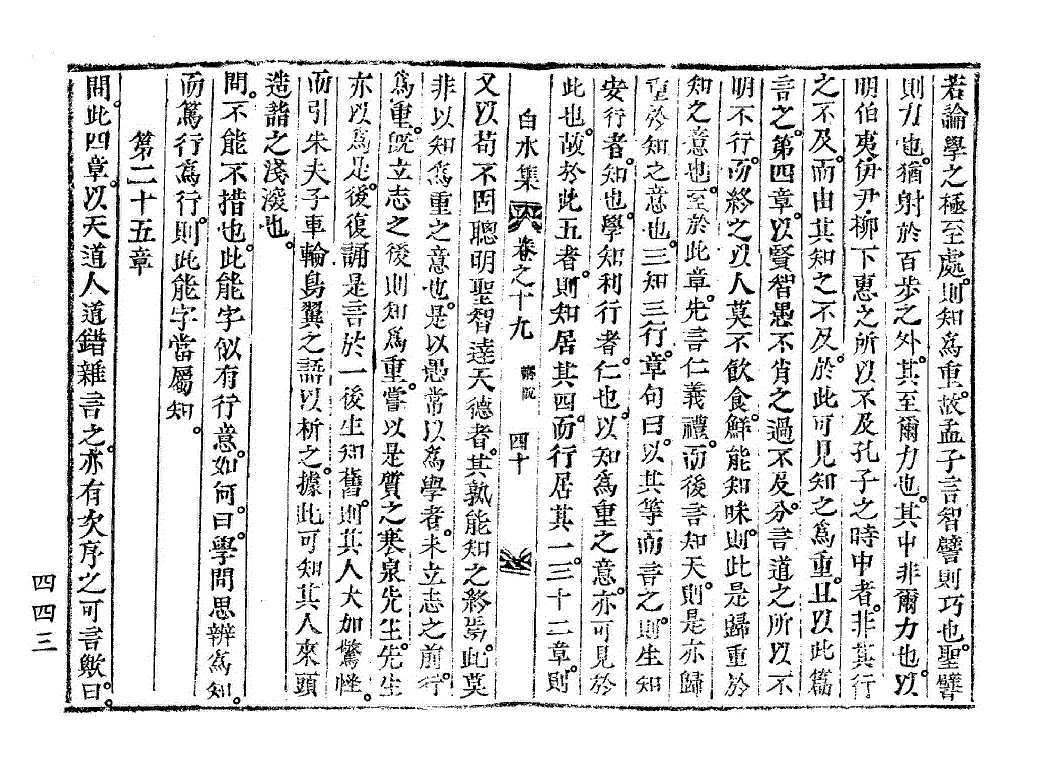 若论学之极至处。则知为重。故孟子言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犹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以明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以不及孔子之时中者。非其行之不及。而由其知之不及。于此可见知之为重。且以此篇言之。第四章。以贤智愚不肖之过不及。分言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终之以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则此是归重于知之意也。至于此章。先言仁义礼。而后言知天。则是亦归重于知之意也。三知三行。章句曰。以其等而言之。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以知为重之意。亦可见于此也。故于此五者。则知居其四。而行居其一。三十二章。则又以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终焉。此莫非以知为重之意也。是以愚常以为学者。未立志之前。行为重。既立志之后则知为重。尝以是质之寒泉先生。先生亦以为是。后复诵是言于一后生知旧。则其人大加惊怪。而引朱夫子车轮鸟翼之语以析之。据此可知其人来头造诣之浅深也。
若论学之极至处。则知为重。故孟子言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犹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以明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以不及孔子之时中者。非其行之不及。而由其知之不及。于此可见知之为重。且以此篇言之。第四章。以贤智愚不肖之过不及。分言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终之以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则此是归重于知之意也。至于此章。先言仁义礼。而后言知天。则是亦归重于知之意也。三知三行。章句曰。以其等而言之。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以知为重之意。亦可见于此也。故于此五者。则知居其四。而行居其一。三十二章。则又以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终焉。此莫非以知为重之意也。是以愚常以为学者。未立志之前。行为重。既立志之后则知为重。尝以是质之寒泉先生。先生亦以为是。后复诵是言于一后生知旧。则其人大加惊怪。而引朱夫子车轮鸟翼之语以析之。据此可知其人来头造诣之浅深也。问。不能不措也。此能字似有行意。如何。曰。学问思辨为知。而笃行为行。则此能字当属知。
第二十五章
问。此四章。以天道人道错杂言之。亦有次序之可言欤。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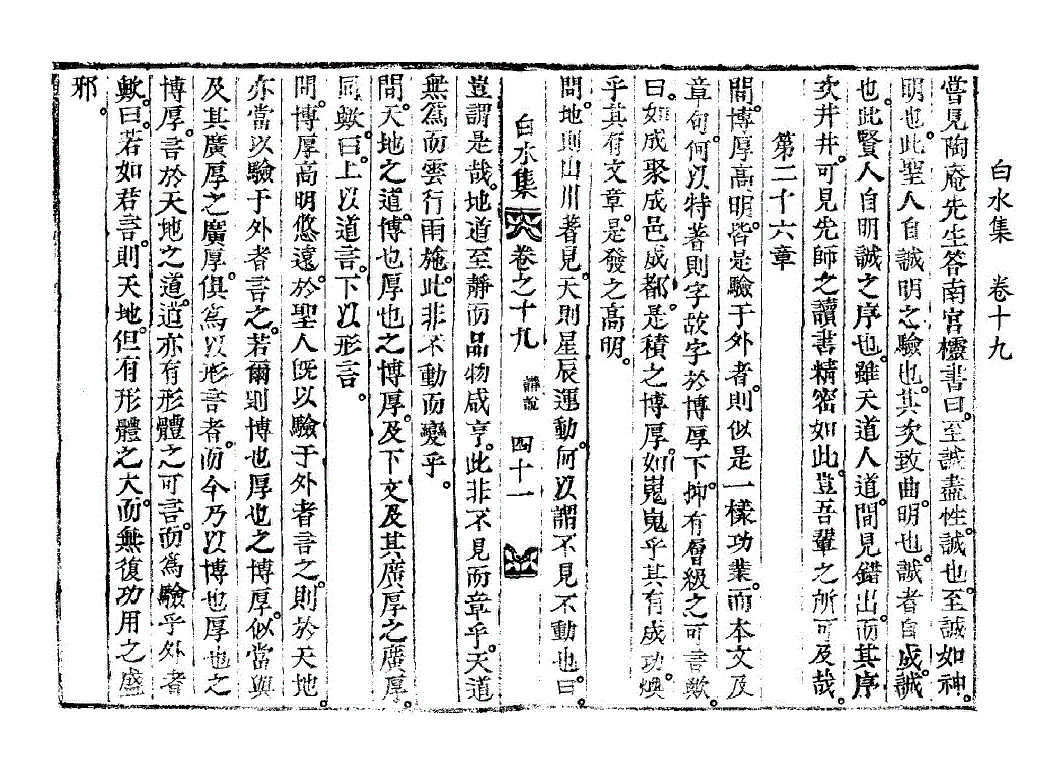 尝见陶庵先生答南宫棂书曰。至诚尽性。诚也。至诚如神。明也。此圣人自诚明之验也。其次致曲。明也。诚者自成。诚也。此贤人自明诚之序也。虽天道人道。间见错出。而其序次井井。可见先师之读书精密如此。岂吾辈之所可及哉。
尝见陶庵先生答南宫棂书曰。至诚尽性。诚也。至诚如神。明也。此圣人自诚明之验也。其次致曲。明也。诚者自成。诚也。此贤人自明诚之序也。虽天道人道。间见错出。而其序次井井。可见先师之读书精密如此。岂吾辈之所可及哉。第二十六章
问。博厚高明。皆是验于外者。则似是一样功业。而本文及章句。何以特著则字故字于博厚下。抑有层级之可言欤。曰。如成聚成邑成都。是积之博厚。如嵬嵬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是发之高明。
问。地则山川著见。天则星辰运动。何以谓不见不动也。曰。岂谓是哉。地道至静而品物咸亨。此非不见而章乎。天道无为而云行雨施。此非不动而变乎。
问。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之博厚。及下文及其广厚之广厚。同欤。曰。上以道言。下以形言。
问。博厚高明悠远。于圣人既以验于外者言之。则于天地。亦当以验于外者言之。若尔则博也厚也之博厚。似当与及其广厚之广厚。俱为以形言者。而今乃以博也厚也之博厚。言于天地之道。道亦有形体之可言。而为验乎外者欤。曰。若如君言。则天地。但有形体之大。而无复功用之盛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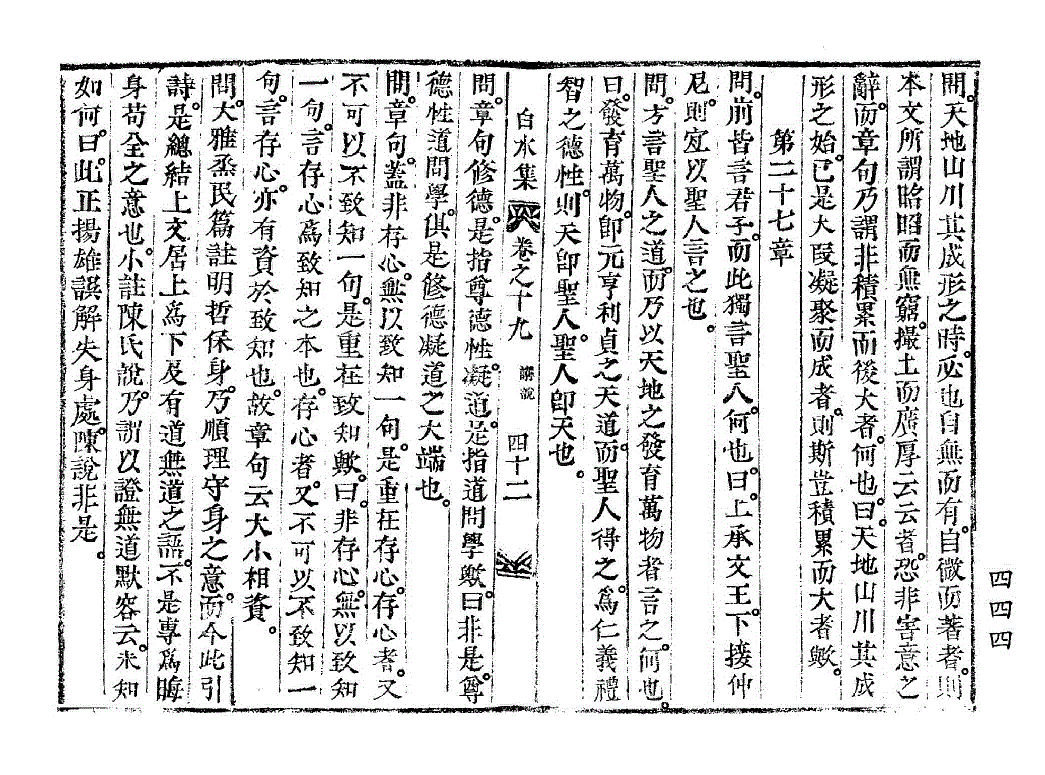 问。天地山川其成形之时。必也自无而有。自微而著者。则本文所谓昭昭而无穷。撮土而广厚云云者。恐非害意之辞。而章句乃谓非积累而后大者。何也。曰。天地山川其成形之始。已是大段凝聚而成者。则斯岂积累而大者欤。
问。天地山川其成形之时。必也自无而有。自微而著者。则本文所谓昭昭而无穷。撮土而广厚云云者。恐非害意之辞。而章句乃谓非积累而后大者。何也。曰。天地山川其成形之始。已是大段凝聚而成者。则斯岂积累而大者欤。第二十七章
问。前皆言君子。而此独言圣人。何也。曰。上承文王。下接仲尼。则宜以圣人言之也。
问。方言圣人之道。而乃以天地之发育万物者言之。何也。曰。发育万物。即元亨利贞之天道。而圣人得之。为仁义礼智之德性。则天即圣人。圣人即天也。
问。章句修德。是指尊德性。凝道。是指道问学欤。曰非是。尊德性道问学。俱是修德凝道之大端也。
问。章句。盖非存心。无以致知一句。是重在存心。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是重在致知欤。曰。非存心。无以致知一句。言存心为致知之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一句。言存心。亦有资于致知也。故章句云大小相资。
问。大雅烝民篇注明哲保身。乃顺理守身之意。而今此引诗。是总结上文居上为下及有道无道之语。不是专为晦身苟全之意也。小注陈氏说。乃谓以證无道默容云。未知如何。曰。此正扬雄误解失身处。陈说非是。
第二十八章
问。行同伦。既与议礼相应。则此依上文。其次序当居第一。而今反居后。何也。下文方言礼乐。礼乐。即与议礼同伦相应。则今同伦之居后。莫是起下文言邪。曰似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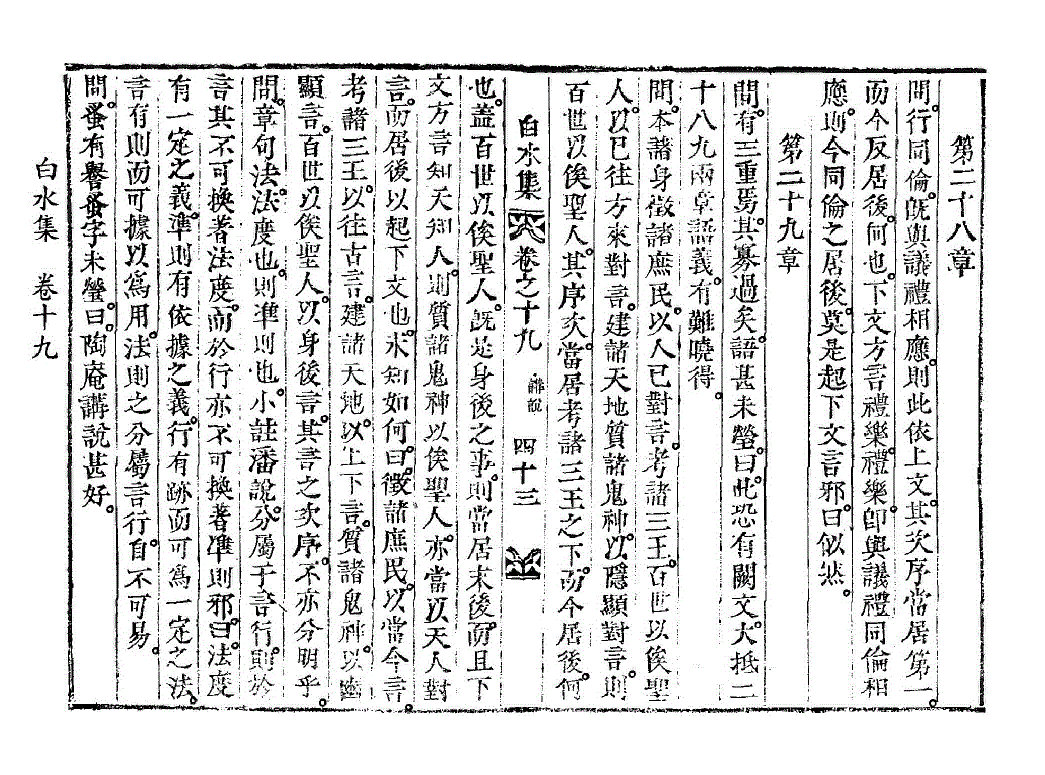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问。有三重焉。其寡过矣。语甚未莹。曰。此恐有阙文。大抵二十八九两章语义。有难晓得。
问。本诸身徵诸庶民。以人己对言。考诸三王。百世以俟圣人。以已往方来对言。建诸天地质诸鬼神。以隐显对言。则百世以俟圣人。其序次。当居考诸三王之下。而今居后。何也。盖百世以俟圣人。既是身后之事。则当居末后。而且下文方言知天知人。则质诸鬼神以俟圣人。亦当以天人对言。而居后以起下文也。未知如何。曰。徵诸庶民。以当今言。考诸三王。以往古言。建诸天地。以上下言。质诸鬼神。以幽显言。百世以俟圣人。以身后言。其言之次序。不亦分明乎。问。章句法。法度也。则准则也。小注潘说。分属于言行。则于言其不可换著法度。而于行亦不可换著准则邪。曰。法度有一定之义。准则有依据之义。行有迹而可为一定之法。言有则而可据以为用。法则之分属言行。自不可易。
问。蚤有誉蚤字未莹。曰。陶庵讲说甚好。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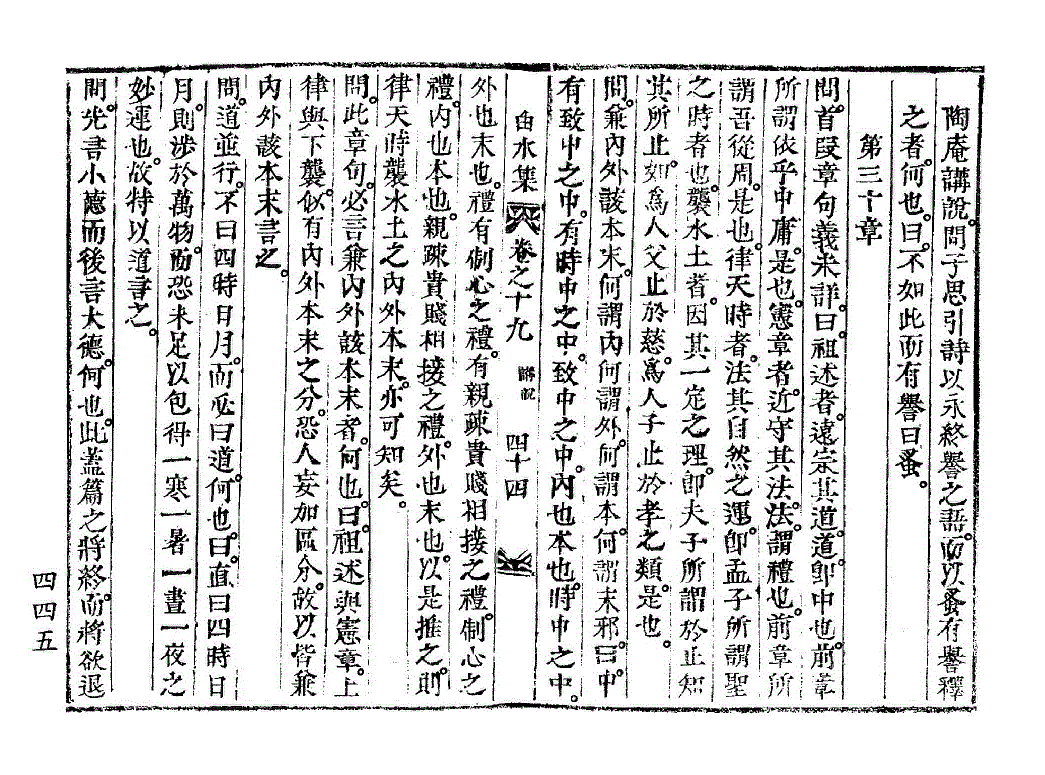 陶庵讲说。问子思引诗以永终誉之语。而以蚤有誉释之者。何也。曰。不如此而有誉曰蚤。
陶庵讲说。问子思引诗以永终誉之语。而以蚤有誉释之者。何也。曰。不如此而有誉曰蚤。第三十章
问。首段章句义未详。曰。祖述者。远宗其道。道。即中也。前章所谓依乎中庸。是也。宪章者。近守其法。法。谓礼也。前章所谓吾从周。是也。律天时者。法其自然之运。即孟子所谓圣之时者也。袭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即夫子所谓于止知其所止。如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之类。是也。
问。兼内外该本末。何谓内何谓外。何谓本。何谓末邪。曰。中有致中之中。有时中之中。致中之中。内也本也。时中之中。外也末也。礼有制心之礼。有亲疏贵贱相接之礼。制心之礼。内也本也。亲疏贵贱相接之礼。外也末也。以是推之。则律天时袭水土之内外本末。亦可知矣。
问。此章句。必言兼内外该本末者。何也。曰。祖述与宪章。上律与下袭。似有内外本末之分。恐人妄加区分。故以皆兼内外该本末言之。
问。道并行。不曰四时日月。而必曰道。何也。曰。直曰四时日月。则涉于万物。而恐未足以包得一寒一暑一昼一夜之妙运也。故特以道言之。
问。先言小德而后言大德。何也。此盖篇之将终。而将欲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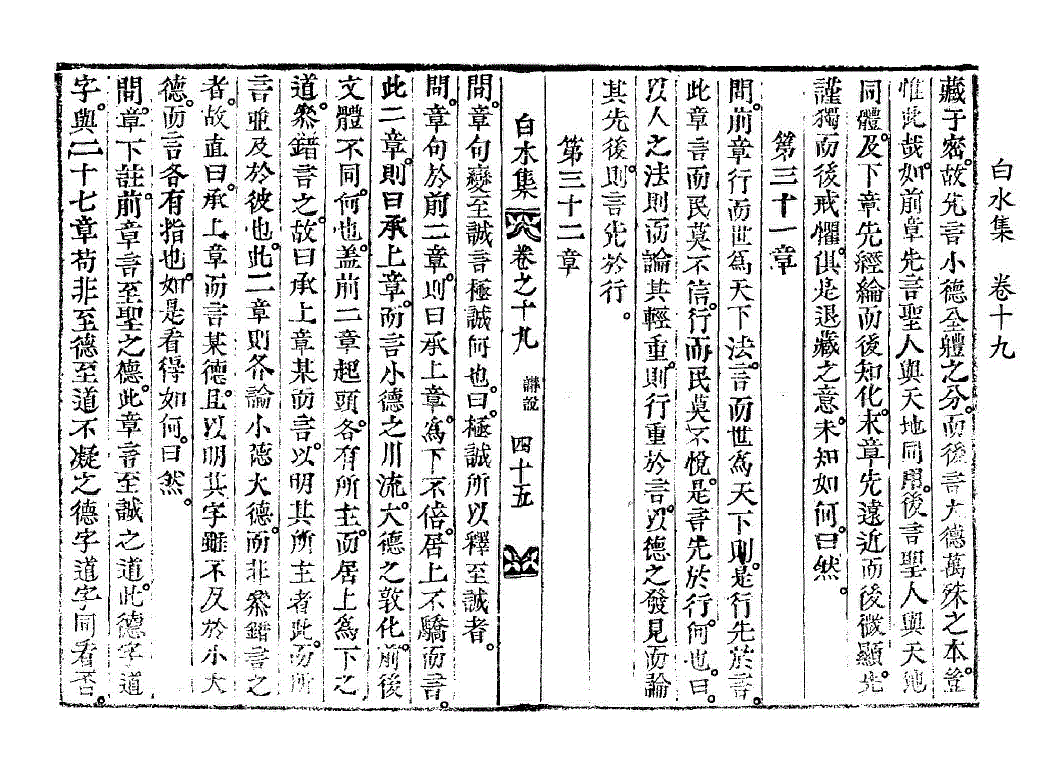 藏于密。故先言小德全体之分。而后言大德万殊之本。岂惟此哉。如前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后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及下章先经纶而后知化。末章先远近而后微显。先谨独而后戒惧。俱是退藏之意。未知如何。曰然。
藏于密。故先言小德全体之分。而后言大德万殊之本。岂惟此哉。如前章先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后言圣人与天地同体。及下章先经纶而后知化。末章先远近而后微显。先谨独而后戒惧。俱是退藏之意。未知如何。曰然。第三十一章
问。前章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是行先于言。此章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是言先于行。何也。曰。以人之法则而论其轻重。则行重于言。以德之发见而论其先后。则言先于行。
第三十二章
问。章句变至诚言极诚何也。曰。极诚所以释至诚者。
问。章句于前二章。则曰承上章。为下不倍。居上不骄而言。此二章。则曰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前后文体不同。何也。盖前二章起头。各有所主。而居上为下之道。参错言之。故曰承上章某而言。以明其所主者此。而所言并及于彼也。此二章则各论小德大德。而非参错言之者。故直曰。承上章而言某德。且以明其字虽不及于小大德。而言各有指也。如是看得如何。曰然。
问。章下注。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此德字道字。与二十七章苟非至德至道不凝之德字道字同看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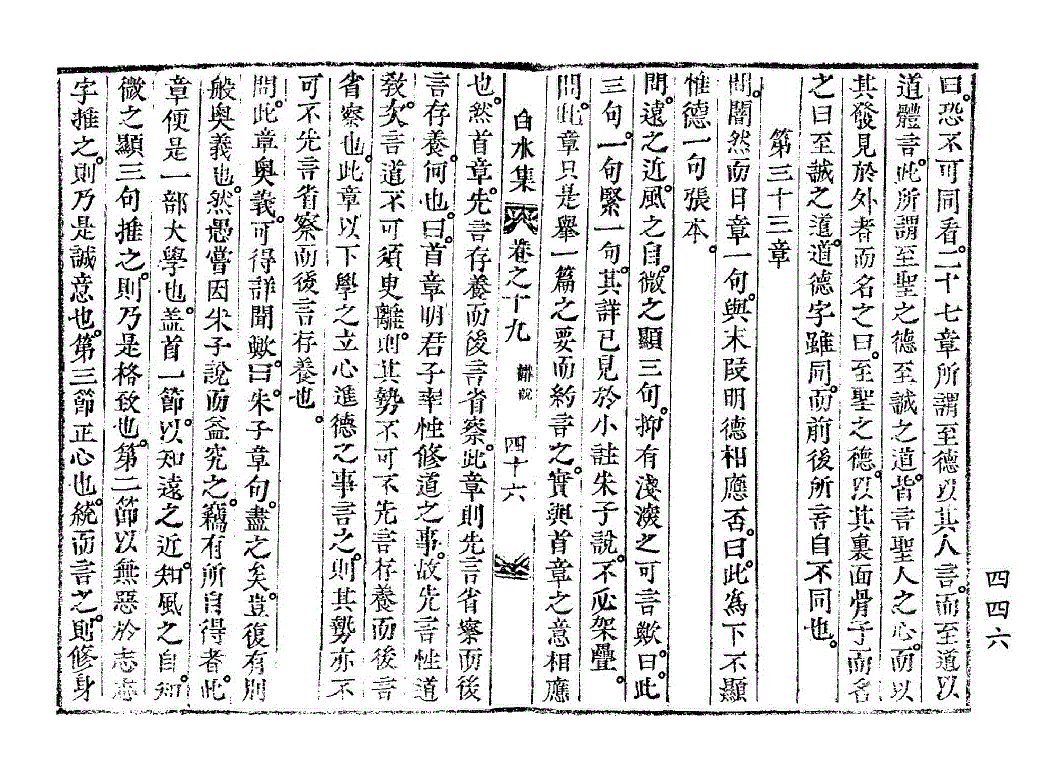 曰。恐不可同看。二十七章所谓至德以其人言。而至道以道体言。此所谓至圣之德至诚之道。皆言圣人之心。而以其发见于外者而名之曰。至圣之德。以其里面骨子而名之曰至诚之道。道德字虽同。而前后所言自不同也。
曰。恐不可同看。二十七章所谓至德以其人言。而至道以道体言。此所谓至圣之德至诚之道。皆言圣人之心。而以其发见于外者而名之曰。至圣之德。以其里面骨子而名之曰至诚之道。道德字虽同。而前后所言自不同也。第三十三章
问。闇然而日章一句。与末段明德相应否。曰。此为下不显惟德一句张本。
问。远之近。风之自。微之显三句。抑有浅深之可言欤。曰。此三句。一句紧一句。其详已见于小注朱子说。不必架叠。
问。此章只是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实与首章之意相应也。然首章。先言存养而后言省察。此章则先言省察而后言存养。何也。曰。首章明君子率性修道之事。故先言性道教。次言道不可须臾离。则其势不可不先言存养而后言省察也。此章以下学之立心进德之事言之。则其势亦不可不先言省察而后言存养也。
问。此章奥义。可得详闻欤。曰。朱子章句。尽之矣。岂复有别般奥义也。然愚尝因朱子说而益究之。窃有所自得者。此章便是一部大学也。盖首一节。以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三句推之。则乃是格致也。第二节以无恶于志志字推之。则乃是诚意也。第三节正心也。统而言之。则修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外集 第 4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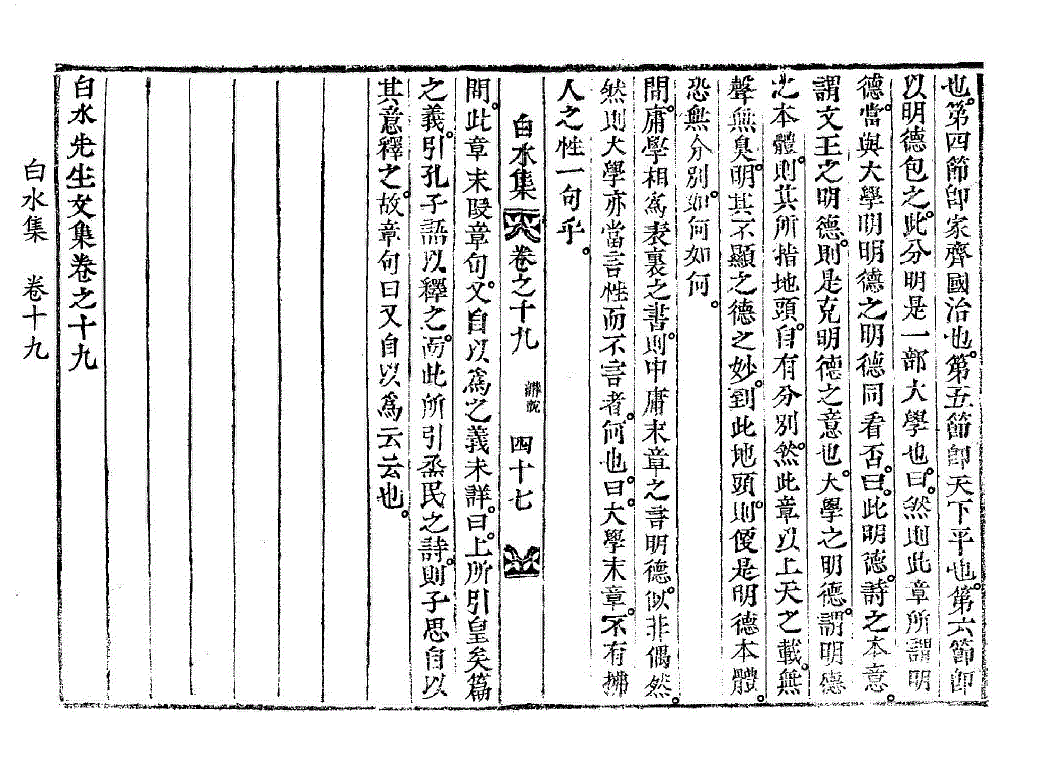 也。第四节即家齐国治也。第五节即天下平也。第六节即以明德包之。此分明是一部大学也。曰。然则此章所谓明德。当与大学明明德之明德同看否。曰。此明德。诗之本意。谓文王之明德。则是克明德之意也。大学之明德。谓明德之本体。则其所指地头。自有分别。然此章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明其不显之德之妙。到此地头。则便是明德本体。恐无分别。如何如何。
也。第四节即家齐国治也。第五节即天下平也。第六节即以明德包之。此分明是一部大学也。曰。然则此章所谓明德。当与大学明明德之明德同看否。曰。此明德。诗之本意。谓文王之明德。则是克明德之意也。大学之明德。谓明德之本体。则其所指地头。自有分别。然此章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明其不显之德之妙。到此地头。则便是明德本体。恐无分别。如何如何。问。庸学相为表里之书。则中庸末章之言明德。似非偶然。然则大学亦当言性而不言者。何也。曰。大学末章。不有拂人之性一句乎。问。此章末段章句。又自以为之义未详。曰。上所引皇矣篇之义。引孔子语以释之。而此所引烝民之诗。则子思自以其意释之。故章句曰又自以为云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