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杂著
杂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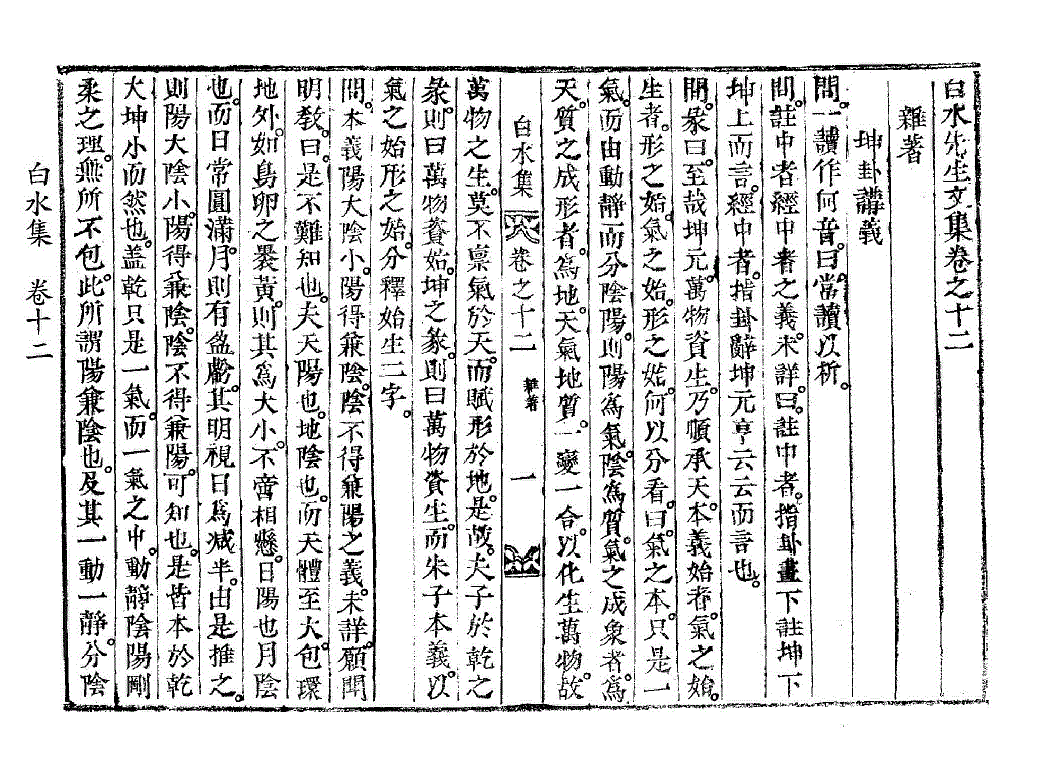 坤卦讲义
坤卦讲义问。⚋读作何音。曰。当读以析。
问。注中者经中者之义。未详。曰。注中者。指卦画下注坤下坤上而言。经中者。指卦辞坤元亨云云而言也。
问。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本义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气之始。形之始。何以分看。曰。气之本。只是一气。而由动静而分阴阳。则阳为气。阴为质。气之成象者。为天。质之成形者。为地。天气地质。一变一合。以化生万物。故万物之生。莫不禀气于天。而赋形于地。是故。夫子于乾之彖。则曰万物资始。坤之彖。则曰万物资生。而朱子本义。以气之始形之始。分释始生二字。
问。本义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之义。未详。愿闻明教。曰。是不难知也。夫天阳也。地阴也。而天体至大。包环地外。如鸟卵之裹黄。则其为大小。不啻相悬。日阳也月阴也。而日常圆满。月则有盈亏。其明视日为减半。由是推之。则阳大阴小。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可知也。是皆本于乾大坤小而然也。盖乾只是一气。而一气之中。动静阴阳刚柔之理。无所不包。此所谓阳兼阴也。及其一动一静。分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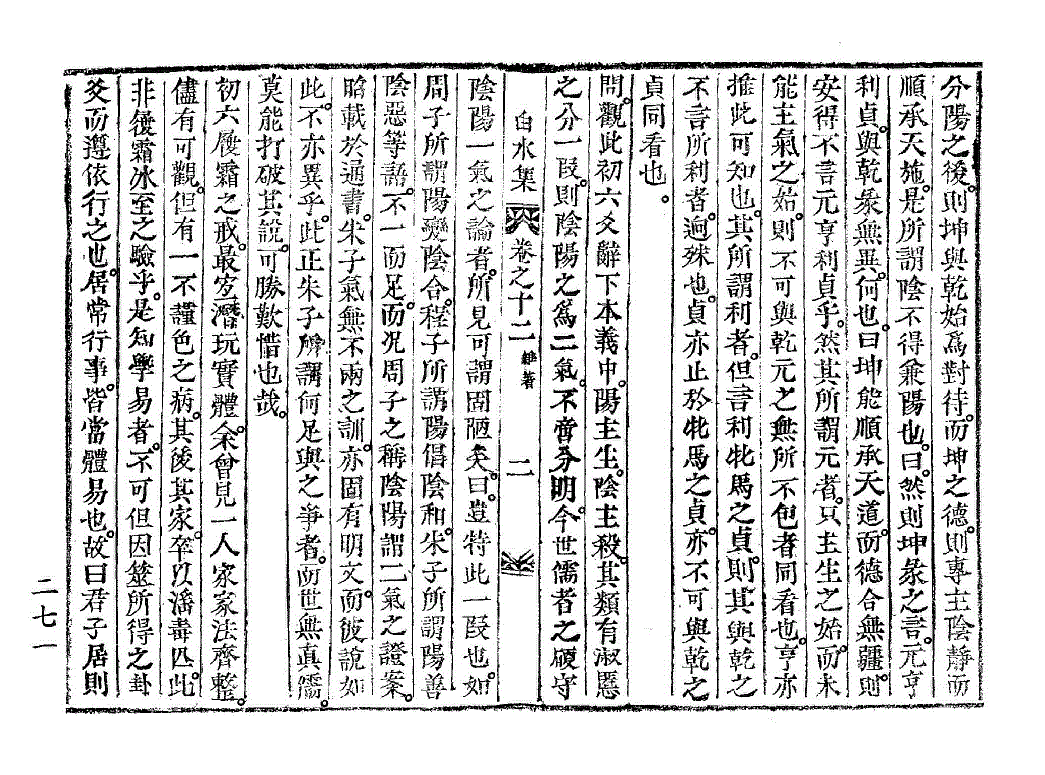 分阳之后。则坤与乾始为对待。而坤之德。则专主阴静而顺承天施。是所谓阴不得兼阳也。曰。然则坤彖之言。元亨利贞。与乾彖无异。何也。曰坤能顺承天道。而德合无疆。则安得不言元亨利贞乎。然其所谓元者。只主生之始。而未能主气之始。则不可与乾元之无所不包者同看也。亨亦推此可知也。其所谓利者。但言利牝马之贞。则其与乾之不言所利者。迥殊也。贞亦止于牝马之贞。亦不可与乾之贞同看也。
分阳之后。则坤与乾始为对待。而坤之德。则专主阴静而顺承天施。是所谓阴不得兼阳也。曰。然则坤彖之言。元亨利贞。与乾彖无异。何也。曰坤能顺承天道。而德合无疆。则安得不言元亨利贞乎。然其所谓元者。只主生之始。而未能主气之始。则不可与乾元之无所不包者同看也。亨亦推此可知也。其所谓利者。但言利牝马之贞。则其与乾之不言所利者。迥殊也。贞亦止于牝马之贞。亦不可与乾之贞同看也。问。观此初六爻辞下本义中。阳主生。阴主杀。其类有淑慝之分一段。则阴阳之为二气。不啻分明。今世儒者之硬守阴阳一气之论者。所见可谓固陋矣。曰。岂特此一段也。如周子所谓阳变阴合。程子所谓阳倡阴和。朱子所谓阳善阴恶等语。不一而足。而况周子之称阴阳谓二气之證案。昭载于通书。朱子气无不两之训。亦固有明文。而彼说如此。不亦异乎。此正朱子所谓何足与之争者。而世无真儒。莫能打破其说。可胜叹惜也哉。
初六履霜之戒。最宜潜玩实体。余曾见一人家家法齐整。尽有可观。但有一不谨色之病。其后其家。卒以淫毒亡。此非履霜冰至之验乎。是知学易者。不可但因筮所得之卦爻而遵依行之也。居常行事。皆当体易也。故曰君子居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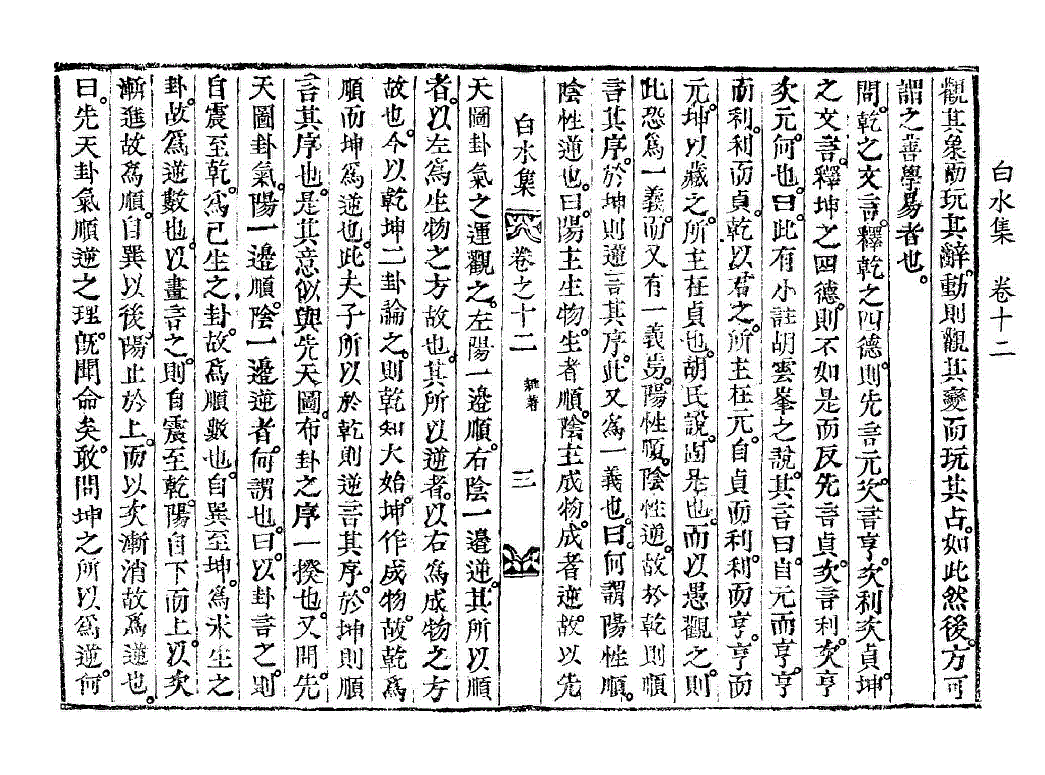 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如此然后。方可谓之善学易者也。
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如此然后。方可谓之善学易者也。问。乾之文言。释乾之四德。则先言元。次言亨。次利次贞。坤之文言。释坤之四德。则不如是而反先言贞。次言利。次亨次元。何也。曰。此有小注胡云峰之说。其言曰。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自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贞也。胡氏说。固是也。而以愚观之。则此恐为一义。而又有一义焉。阳性顺。阴性逆。故于乾则顺言其序。于坤则逆言其序。此又为一义也。曰。何谓阳性顺。阴性逆也。曰。阳主生物。生者顺。阴主成物。成者逆。故以先天图卦气之运观之。左阳一边顺。右阴一边逆。其所以顺者。以左为生物之方故也。其所以逆者。以右为成物之方故也。今以乾坤二卦论之。则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故乾为顺而坤为逆也。此夫子所以于乾则逆言其序。于坤则顺言其序也。是其意似与先天图。布卦之序一揆也。又问。先天图卦气。阳一边顺。阴一边逆者。何谓也。曰。以卦言之。则自震至乾。为已生之卦。故为顺数也。自巽至坤。为未生之卦。故为逆数也。以画言之。则自震至乾。阳自下而上。以次渐进故为顺。自巽以后。阳止于上。而以次渐消故为逆也。曰。先天卦气顺逆之理。既闻命矣。敢问坤之所以为逆。何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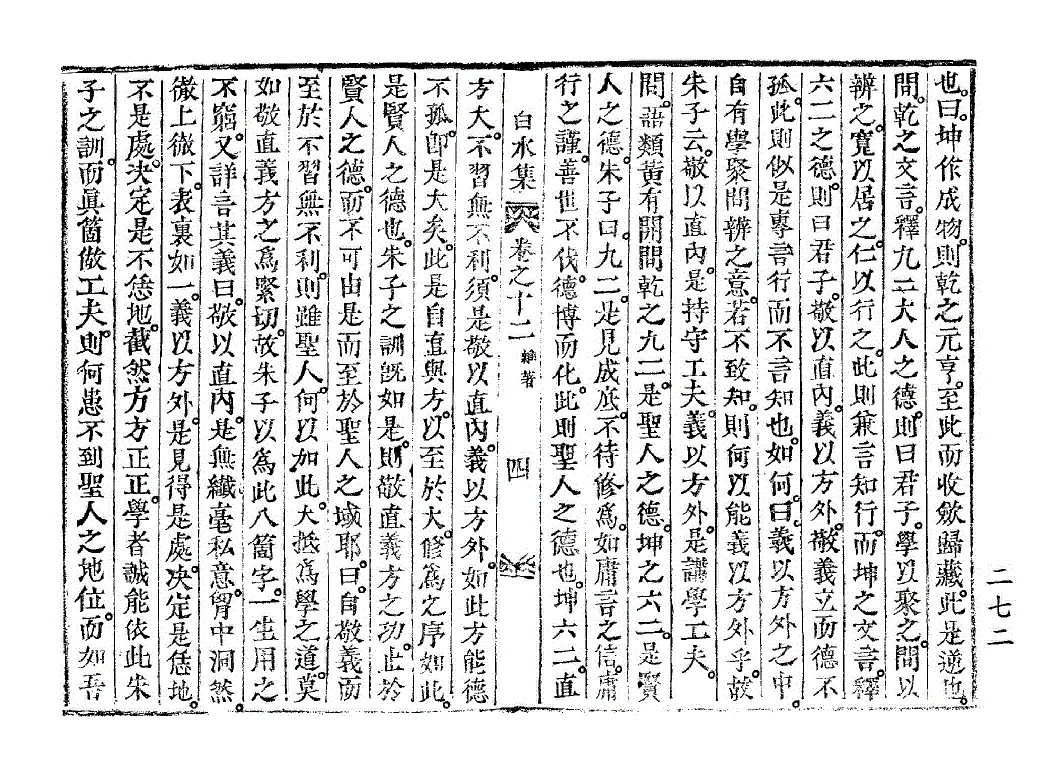 也。曰。坤作成物。则乾之元亨。至此而收敛归藏。此是逆也。
也。曰。坤作成物。则乾之元亨。至此而收敛归藏。此是逆也。问。乾之文言。释九二大人之德。则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此则兼言知行。而坤之文言。释六二之德。则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此则似是专言行而不言知也。如何。曰。义以方外之中。自有学聚问辨之意。若不致知。则何以能义以方外乎。故朱子云。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工夫。
问。语类黄有开问乾之九二。是圣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贤人之德。朱子曰。九二。是见成底。不待修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则圣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须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即是大矣。此是自直与方。以至于大。修为之序如此。是贤人之德也。朱子之训既如是。则敬直义方之功。止于贤人之德。而不可由是而至于圣人之域耶。曰。自敬义而至于不习无不利。则虽圣人。何以加此。大抵为学之道。莫如敬直义方之为紧切。故朱子以为此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又详言其义曰。敬以直内。是无纤毫私意。胸中洞然。彻上彻下。表里如一。义以方外。是见得是处。决定是恁地。不是处。决定是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学者诚能依此朱子之训。而真个做工夫。则何患不到圣人之地位。而如吾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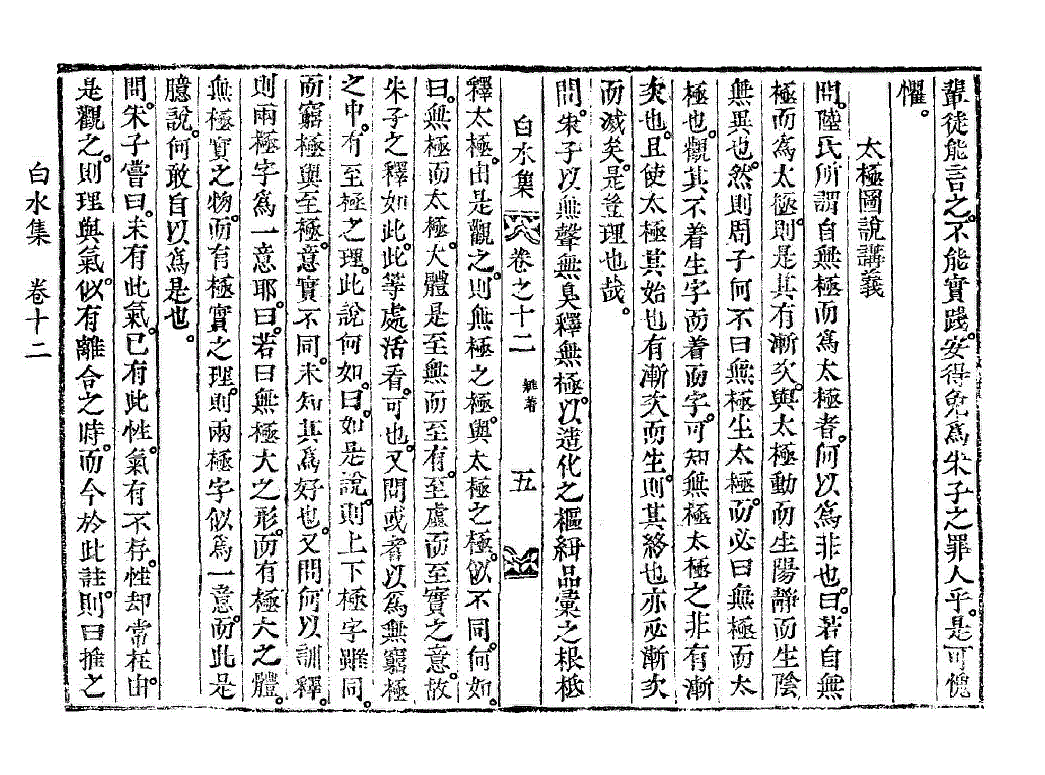 辈徒能言之。不能实践。安得免为朱子之罪人乎。是可愧惧。
辈徒能言之。不能实践。安得免为朱子之罪人乎。是可愧惧。太极图说讲义
问。陆氏所谓自无极而为太极者。何以为非也。曰。若自无极而为太极。则是其有渐次。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无异也。然则周子何不曰无极生太极。而必曰无极而太极也。观其不着生字而着而字。可知无极太极之非有渐次也。且使太极其始也有渐次而生。则其终也亦必渐次而灭矣。是岂理也哉。
问。朱子以无声无臭释无极。以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释太极。由是观之。则无极之极。与太极之极。似不同。何如。曰。无极而太极。大体是至无而至有。至虚而至实之意。故朱子之释如此。此等处活看。可也。又问或者以为无穷极之中。有至极之理。此说何如。曰。如是说。则上下极字虽同。而穷极与至极。意实不同。未知其为好也。又问何以训释。则两极字为一意耶。曰。若曰无极大之形。而有极大之体。无极实之物。而有极实之理。则两极字似为一意。而此是臆说。何敢自以为是也。
问。朱子尝曰。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由是观之。则理与气。似有离合之时。而今于此注。则曰推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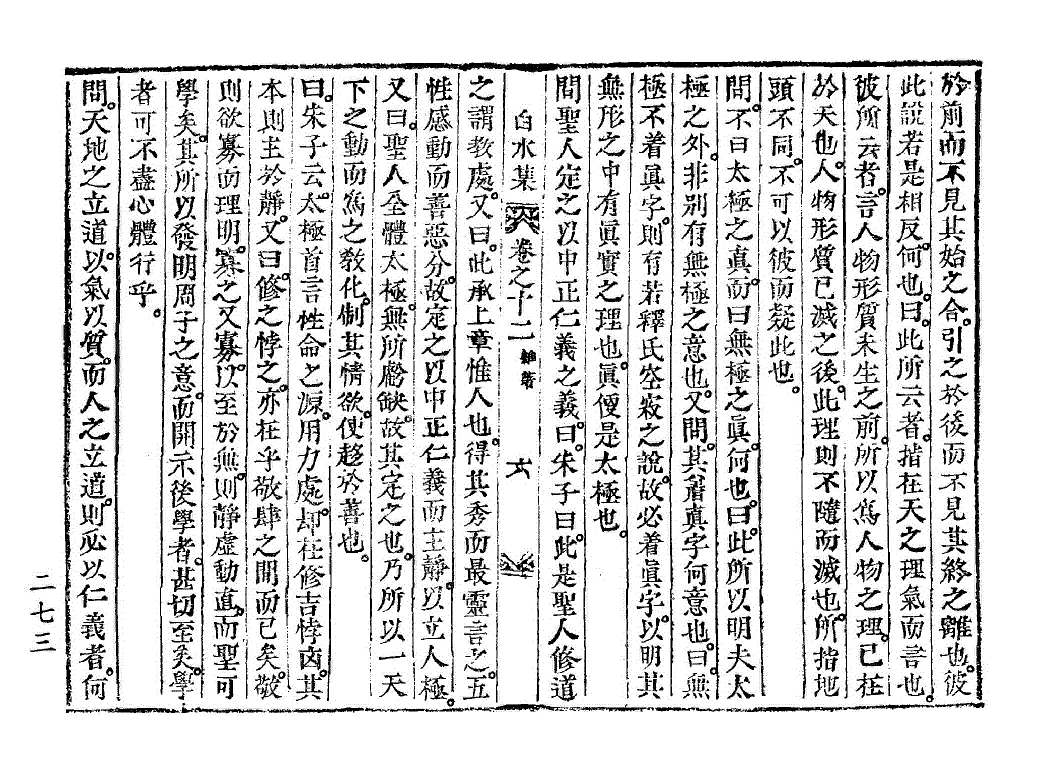 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彼此说若是相反。何也。曰。此所云者。指在天之理气而言也。彼所云者。言人物形质未生之前。所以为人物之理。已在于天也。人物形质已灭之后。此理则不随而灭也。所指地头不同。不可以彼而疑此也。
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彼此说若是相反。何也。曰。此所云者。指在天之理气而言也。彼所云者。言人物形质未生之前。所以为人物之理。已在于天也。人物形质已灭之后。此理则不随而灭也。所指地头不同。不可以彼而疑此也。问。不曰太极之真。而曰无极之真。何也。曰。此所以明夫太极之外。非别有无极之意也。又问。其着真字何意也。曰。无极不着真字。则有若释氏空寂之说。故必着真字。以明其无形之中有真实之理也。真便是太极也。
问。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之义。曰。朱子曰。此是圣人修道之谓教处。又曰。此承上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言之。五性感动而善恶分。故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以立人极。又曰。圣人全体太极。无所亏缺。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动而为之教化。制其情欲。使趍于善也。
曰。朱子云。太极首言性命之源。用力处。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则主于静。又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间而已矣。敬则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静虚动直。而圣可学矣。其所以发明周子之意。而开示后学者。甚切至矣。学者可不尽心体行乎。
问。天地之立道。以气以质。而人之立道。则必以仁义者。何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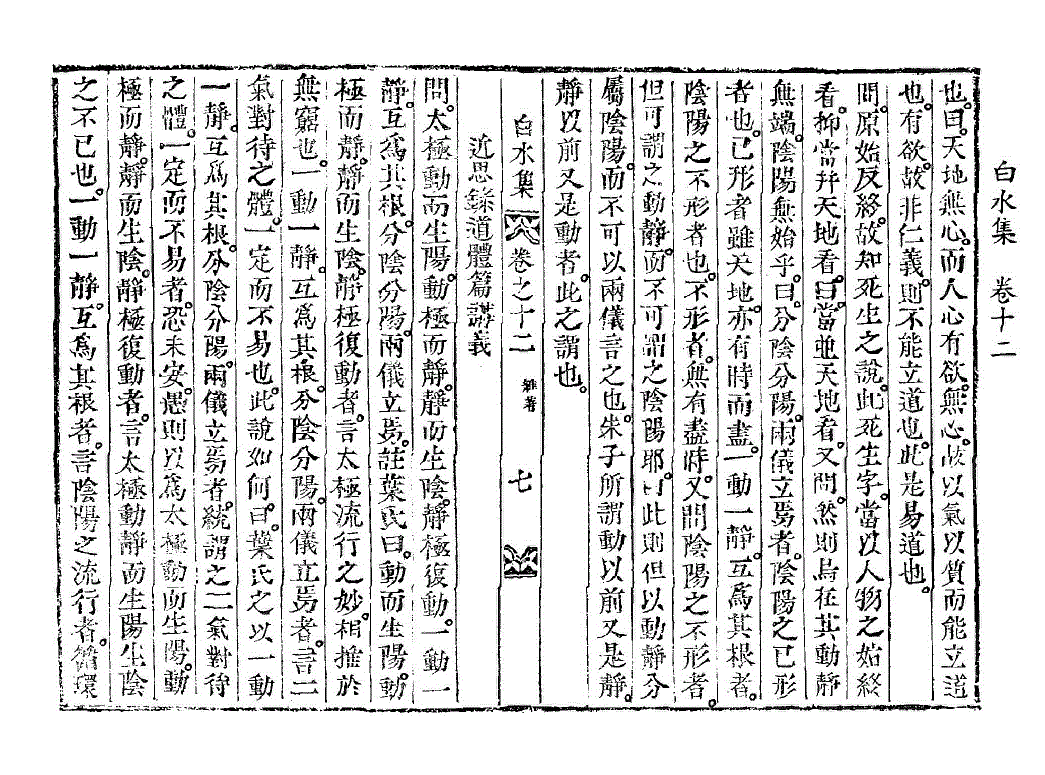 也。曰。天地无心。而人心有欲。无心。故以气以质而能立道也。有欲。故非仁义。则不能立道也。此是易道也。
也。曰。天地无心。而人心有欲。无心。故以气以质而能立道也。有欲。故非仁义。则不能立道也。此是易道也。问。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此死生字。当以人物之始终看。抑当并天地看。曰。当并天地看。又问。然则乌在其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乎。曰。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阴阳之已形者也。已形者虽天地。亦有时而尽。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阴阳之不形者也。不形者。无有尽时。又问阴阳之不形者。但可谓之动静。而不可谓之阴阳耶。曰此则但以动静分属阴阳。而不可以两仪言之也。朱子所谓动以前又是静。静以前又是动者。此之谓也。
近思录道体篇讲义
问。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注叶氏曰。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者。言太极流行之妙。相推于无穷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言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也。此说如何。曰。叶氏之以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统谓之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者。恐未安。愚则以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者。言太极动静而生阳生阴之不已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言阴阳之流行者。循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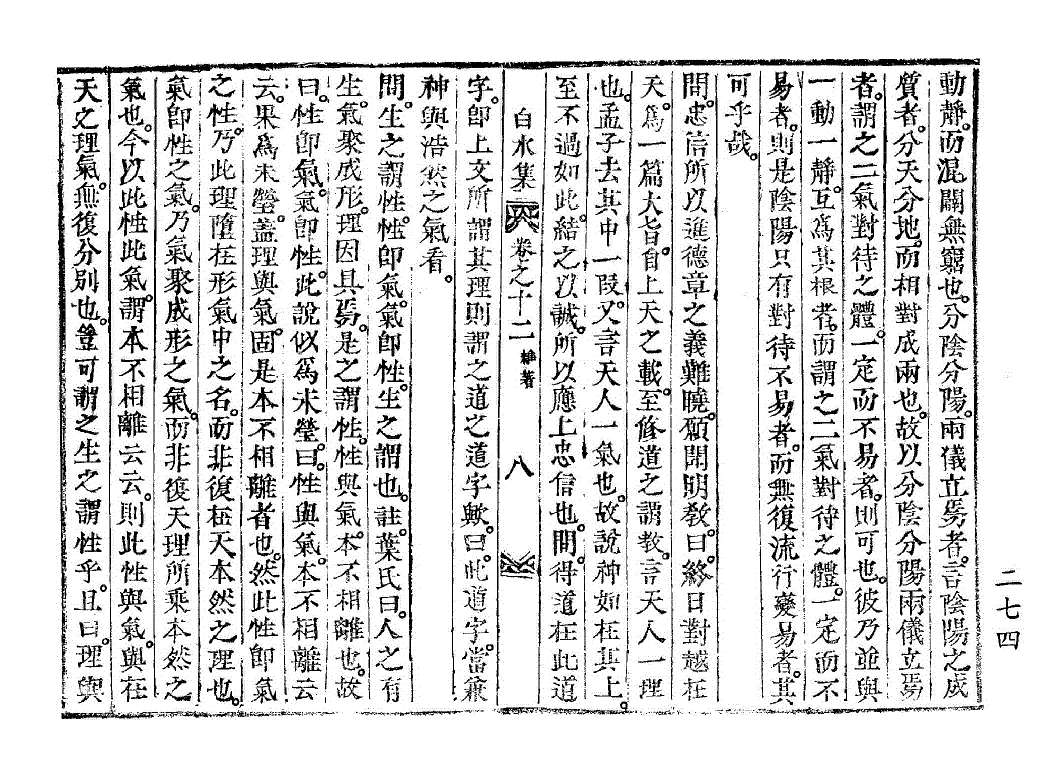 动静。而混辟无穷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言阴阳之成质者。分天分地。而相对成两也。故以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谓之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者。则可也。彼乃并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而谓之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者。则是阴阳只有对待不易者。而无复流行变易者。其可乎哉。
动静。而混辟无穷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言阴阳之成质者。分天分地。而相对成两也。故以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谓之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者。则可也。彼乃并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而谓之二气对待之体。一定而不易者。则是阴阳只有对待不易者。而无复流行变易者。其可乎哉。问。忠信所以进德章之义难晓。愿闻明教。曰。终日对越在天。为一篇大旨。自上天之载。至修道之谓教。言天人一理也。孟子去其中一段。又言天人一气也。故说神如在其上。至不过如此。结之以诚。所以应上忠信也。问。得道在此道字。即上文所谓其理则谓之道之道字欤。曰。此道字。当兼神与浩然之气看。
问。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注。叶氏曰。人之有生。气聚成形。理因具焉。是之谓性。性与气。本不相离也。故曰。性即气。气即性。此说似为未莹。曰。性与气。本不相离云云。果为未莹。盖理与气。固是本不相离者也。然此性即气之性。乃此理堕在形气中之名。而非复在天本然之理也。气即性之气。乃气聚成形之气。而非复天理所乘本然之气也。今以此性此气。谓本不相离云云。则此性与气。与在天之理气。无复分别也。岂可谓之生之谓性乎。且曰。理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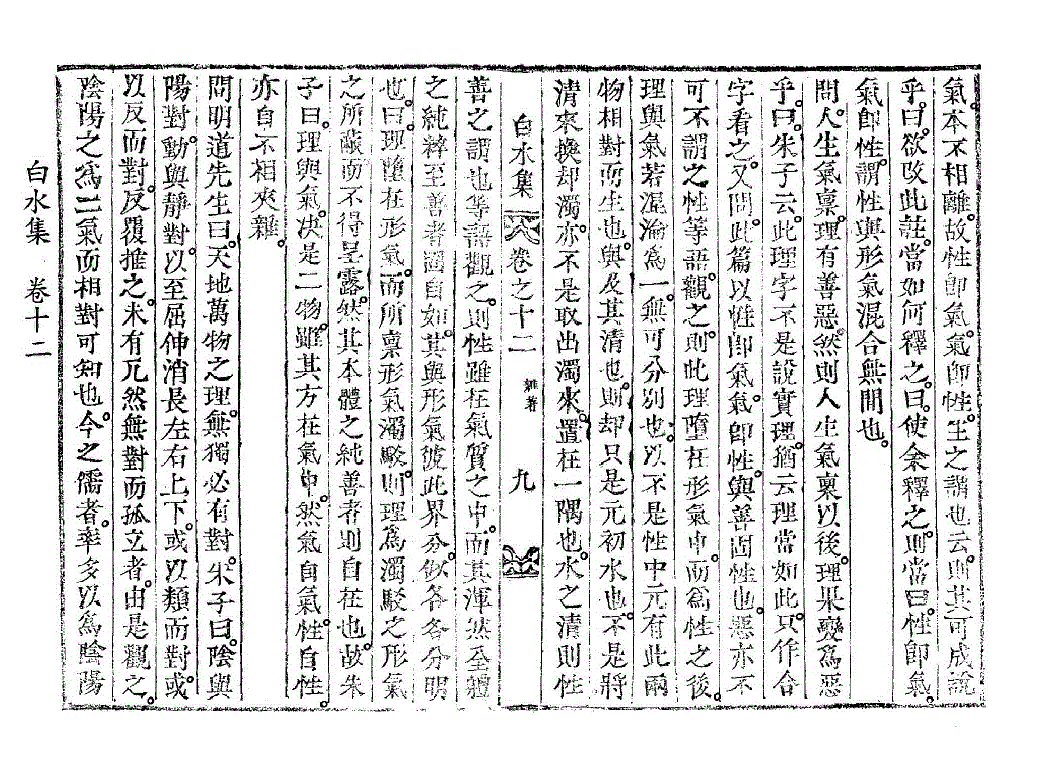 气。本不相离。故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云。则其可成说乎。曰。欲改此注。当如何释之。曰。使余释之。则当曰。性即气。气即性。谓性与形气混合无间也。
气。本不相离。故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云。则其可成说乎。曰。欲改此注。当如何释之。曰。使余释之。则当曰。性即气。气即性。谓性与形气混合无间也。问。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则人生气禀以后。理果变为恶乎。曰。朱子云。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只作合字看之。又问。此篇以性即气。气即性。与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等语。观之。则此理堕在形气中。而为性之后。理与气若混沦为一。无可分别也。以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与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等语观之。则性虽在气质之中。而其浑然全体之纯粹至善者固自如。其与形气彼此界分。似各各分明也。曰。理堕在形气。而所禀形气浊驳。则理为浊驳之形气之所蔽。而不得呈露。然其本体之纯善者则自在也。故朱子曰。理与气。决是二物。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
问。明道先生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朱子曰。阴与阳对。动与静对。以至屈伸消长左右上下。或以类而对。或以反而对。反覆推之。未有兀然无对而孤立者。由是观之。阴阳之为二气而相对可知也。今之儒者。率多以为阴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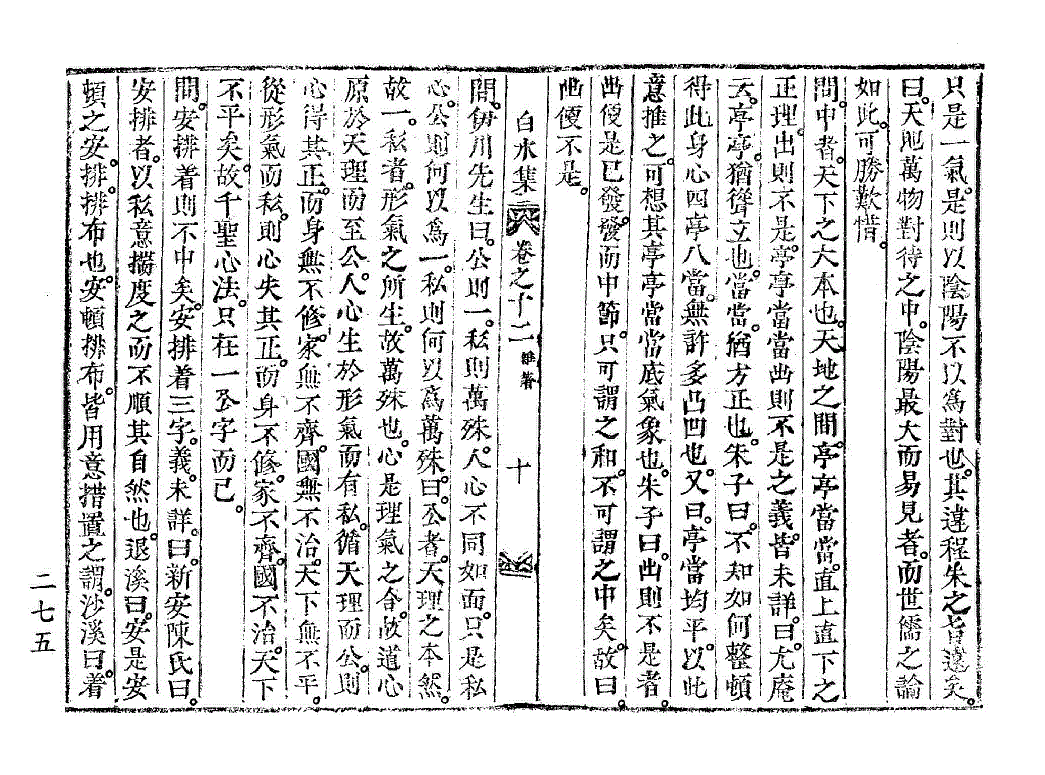 只是一气。是则以阴阳不以为对也。其违程,朱之旨远矣。曰。天地万物对待之中。阴阳最大而易见者。而世儒之论如此。可胜叹惜。
只是一气。是则以阴阳不以为对也。其违程,朱之旨远矣。曰。天地万物对待之中。阴阳最大而易见者。而世儒之论如此。可胜叹惜。问。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间。亭亭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亭亭当当出则不是之义。皆未详。曰。尤庵云。亭亭。犹耸立也。当当。犹方正也。朱子曰。不知如何整顿得此身心四亭八当。无许多凸凹也。又曰。亭当均平。以此意推之。可想其亭亭当当底气象也。朱子曰。出则不是者。出便是已发。发而中节。只可谓之和。不可谓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问。伊川先生曰。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公则何以为一。私则何以为万殊。曰。公者。天理之本然。故一。私者。形气之所生。故万殊也。心是理气之合。故道心原于天理而至公。人心生于形气而有私。循天理而公。则心得其正。而身无不修。家无不齐。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从形气而私。则心失其正。而身不修。家不齐。国不治。天下不平矣。故千圣心法。只在一公字而已。
问。安排着则不中矣。安排着三字。义。未详。曰。新安陈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顺其自然也。退溪曰。安是安顿之安。排。排布也。安顿排布。皆用意措置之谓。沙溪曰。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6H 页
 犹为也。
犹为也。问。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此段。不能无疑。孟子于四端。皆着心字。孟子非欤。曰。不观本注所引朱子说乎。朱子曰。既发。不可谓之非心。但有不善。则非心之本体。此其补说也。
问。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此段文义难晓。曰。朱子云。此句是张思叔所记。疑有欠阙处。又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禀赋。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恻隐之心在人。亦为生道也。以此等语及本注所引朱子语推之。则程子本义。庶可见得矣。
问。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此段义未详。盖只言坱然太虚。此虚实动静之机云云。则似好。而乃以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并言于坱然太虚之下。则虚实动静阴阳刚柔。已在于升降飞扬之中。何可谓之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乎。机始二字。恐不衬贴。如何。曰。此可谓善发问也。然此非可疑之言也。盖坱然太虚。言其体也。升降飞扬。未尝止息。言其用也。惟其体用如是底。所以有虚实动静。所以生阴阳刚柔。则其以是谓之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不亦宜乎。若如贤说。只曰坱然太虚。此虚实动静之机云。则是言体而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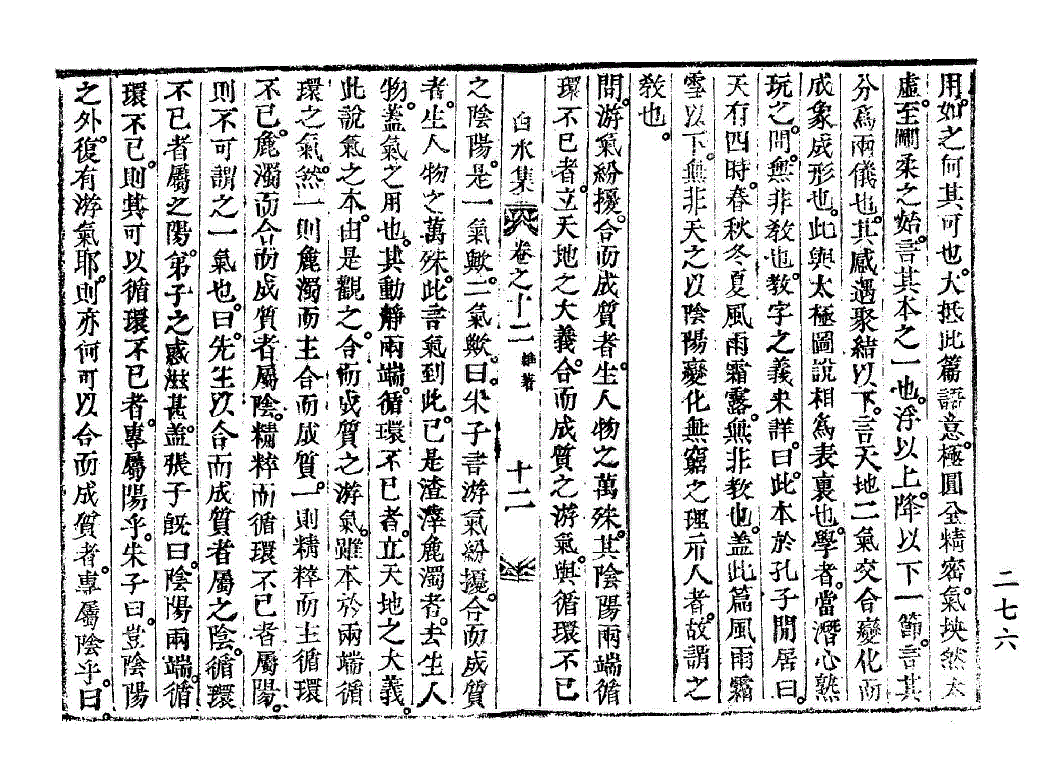 用。如之何其可也。大抵此篇语意。极圆全精密。气坱然太虚。至刚柔之始。言其本之一也。浮以上。降以下一节。言其分为两仪也。其感遇聚结以下。言天地二气交合变化而成象成形也。此与太极图说相为表里也。学者。当潜心熟玩之。
用。如之何其可也。大抵此篇语意。极圆全精密。气坱然太虚。至刚柔之始。言其本之一也。浮以上。降以下一节。言其分为两仪也。其感遇聚结以下。言天地二气交合变化而成象成形也。此与太极图说相为表里也。学者。当潜心熟玩之。问。无非教也。教字之义未详。曰。此本于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盖此篇风雨霜雪以下。无非天之以阴阳变化无穷之理示人者。故谓之教也。
问。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合而成质之游气。与循环不已之阴阳。是一气欤。二气欤。曰。朱子言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此言气到此。已是渣滓粗浊者。去生人物。盖气之用也。其动静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此说气之本。由是观之。合而成质之游气。虽本于两端循环之气。然一则粗浊而主合而成质。一则精粹而主循环不已。粗浊而合而成质者属阴。精粹而循环不已者属阳。则不可谓之一气也。曰。先生以合而成质者属之阴。循环不已者属之阳。弟子之惑滋甚。盖张子既曰。阴阳两端。循环不已。则其可以循环不已者。专属阳乎。朱子曰。岂阴阳之外。复有游气耶。则亦何可以合而成质者。专属阴乎。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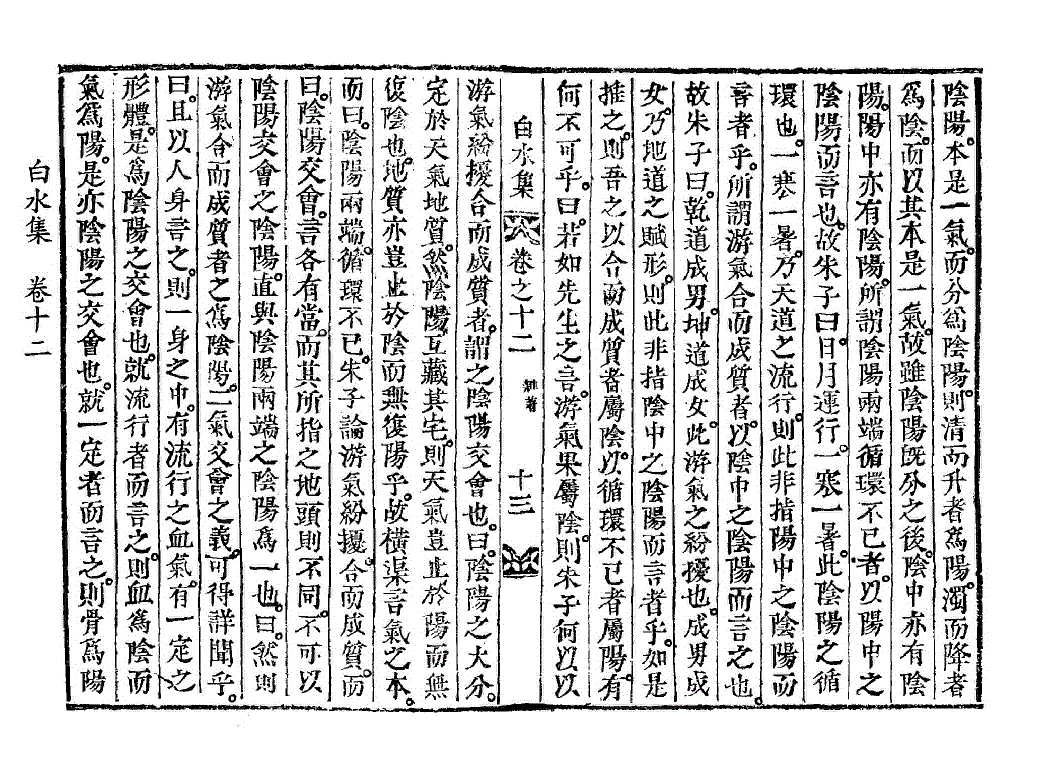 阴阳。本是一气。而分为阴阳。则清而升者为阳。浊而降者为阴。而以其本是一气。故虽阴阳既分之后。阴中亦有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所谓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以阳中之阴阳而言也。故朱子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此阴阳之循环也。一寒一暑。乃天道之流行。则此非指阳中之阴阳而言者乎。所谓游气合而成质者。以阴中之阴阳而言之也。故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气之纷扰也。成男成女。乃地道之赋形。则此非指阴中之阴阳而言者乎。如是推之。则吾之以合而成质者属阴。以循环不已者属阳。有何不可乎。曰。若如先生之言。游气果属阴。则朱子何以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谓之阴阳交会也。曰。阴阳之大分。定于天气地质。然阴阳互藏其宅。则天气岂止于阳而无复阴也。地质亦岂止于阴而无复阳乎。故横渠言气之本。而曰。阴阳两端。循环不已。朱子论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而曰。阴阳交会。言各有当。而其所指之地头则不同。不可以阴阳交会之阴阳。直与阴阳两端之阴阳为一也。曰。然则游气合而成质者之为阴阳。二气交会之义。可得详闻乎。曰。且以人身言之。则一身之中。有流行之血气。有一定之形体。是为阴阳之交会也。就流行者而言之。则血为阴而气为阳。是亦阴阳之交会也。就一定者而言之。则骨为阳
阴阳。本是一气。而分为阴阳。则清而升者为阳。浊而降者为阴。而以其本是一气。故虽阴阳既分之后。阴中亦有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所谓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以阳中之阴阳而言也。故朱子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此阴阳之循环也。一寒一暑。乃天道之流行。则此非指阳中之阴阳而言者乎。所谓游气合而成质者。以阴中之阴阳而言之也。故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气之纷扰也。成男成女。乃地道之赋形。则此非指阴中之阴阳而言者乎。如是推之。则吾之以合而成质者属阴。以循环不已者属阳。有何不可乎。曰。若如先生之言。游气果属阴。则朱子何以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谓之阴阳交会也。曰。阴阳之大分。定于天气地质。然阴阳互藏其宅。则天气岂止于阳而无复阴也。地质亦岂止于阴而无复阳乎。故横渠言气之本。而曰。阴阳两端。循环不已。朱子论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而曰。阴阳交会。言各有当。而其所指之地头则不同。不可以阴阳交会之阴阳。直与阴阳两端之阴阳为一也。曰。然则游气合而成质者之为阴阳。二气交会之义。可得详闻乎。曰。且以人身言之。则一身之中。有流行之血气。有一定之形体。是为阴阳之交会也。就流行者而言之。则血为阴而气为阳。是亦阴阳之交会也。就一定者而言之。则骨为阳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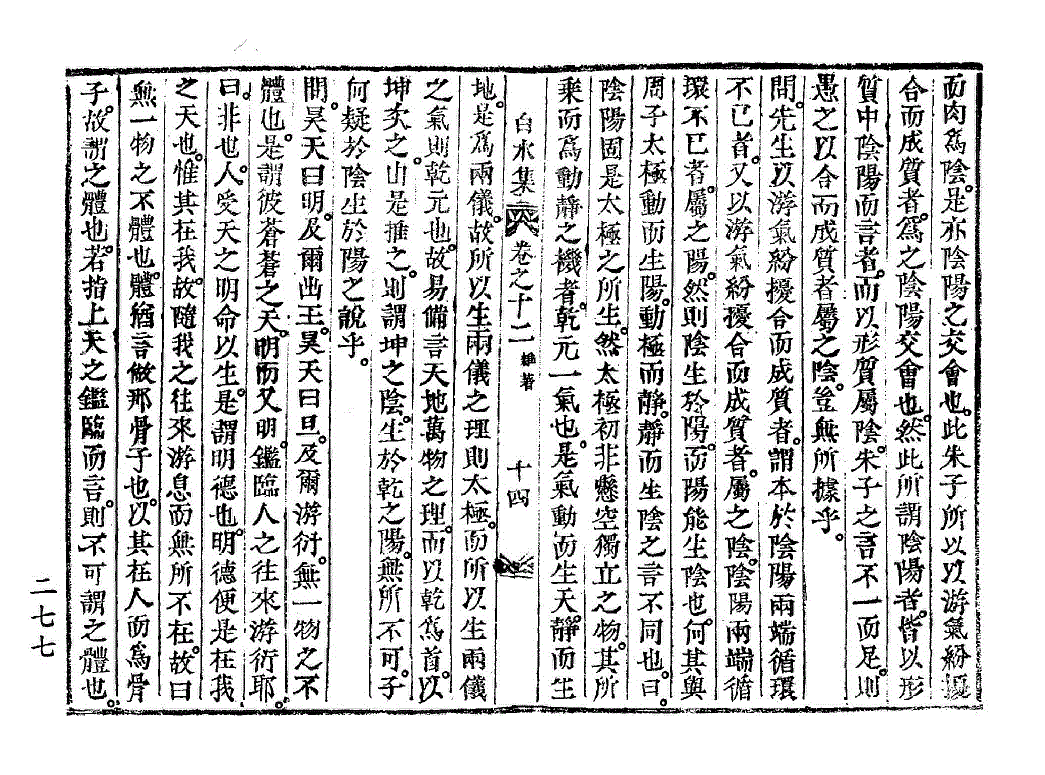 而肉为阴。是亦阴阳之交会也。此朱子所以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为之阴阳交会也。然此所谓阴阳者。皆以形质中阴阳而言者。而以形质属阴。朱子之言不一而足。则愚之以合而成质者属之阴。岂无所据乎。
而肉为阴。是亦阴阳之交会也。此朱子所以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为之阴阳交会也。然此所谓阴阳者。皆以形质中阴阳而言者。而以形质属阴。朱子之言不一而足。则愚之以合而成质者属之阴。岂无所据乎。问。先生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谓本于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又以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属之阴。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属之阳。然则阴生于阳。而阳能生阴也。何其与周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之言不同也。曰。阴阳固是太极之所生。然太极初非悬空独立之物。其所乘而为动静之机者。乾元一气也。是气动而生天。静而生地。是为两仪。故所以生两仪之理则太极。而所以生两仪之气则乾元也。故易备言天地万物之理。而以乾为首。以坤次之。由是推之。则谓坤之阴。生于乾之阳。无所不可。子何疑于阴生于阳之说乎。
问。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一物之不体也。是谓彼苍苍之天。明而又明。鉴临人之往来游衍耶。曰。非也。人受天之明命以生。是谓明德也。明德便是在我之天也。惟其在我。故随我之往来游息而无所不在。故曰无一物之不体也。体犹言做那骨子也。以其在人而为骨子。故谓之体也。若指上天之鉴临而言。则不可谓之体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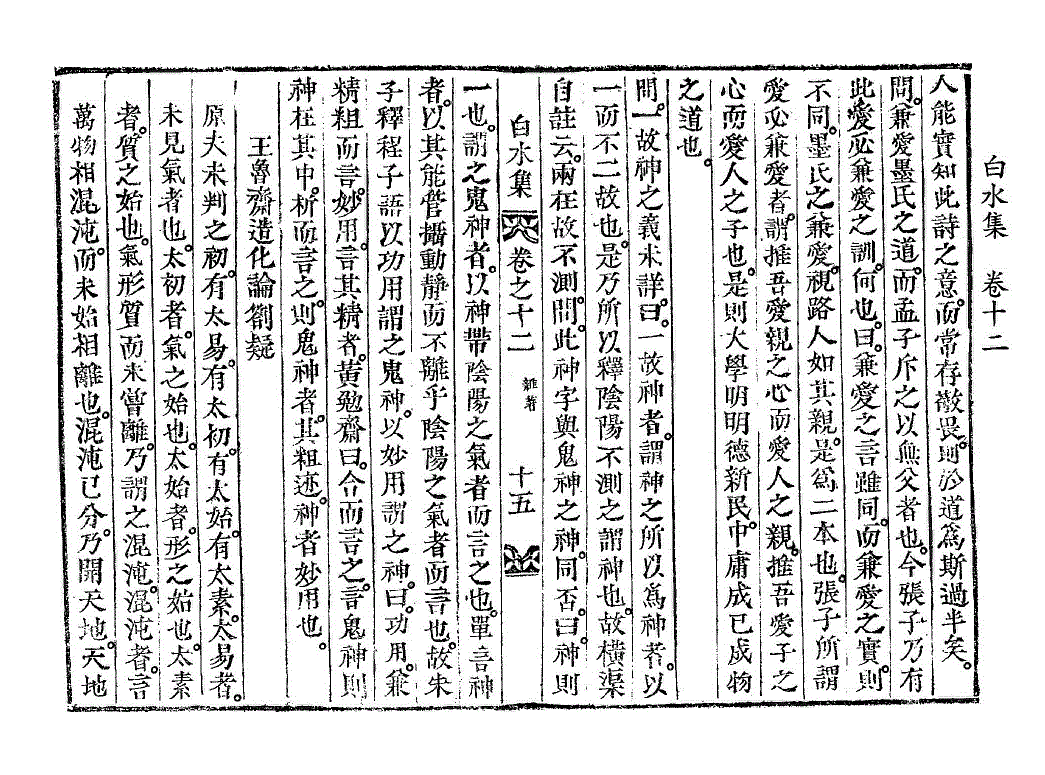 人能实知此诗之意。而常存敬畏。则于道为斯过半矣。
人能实知此诗之意。而常存敬畏。则于道为斯过半矣。问。兼爱墨氏之道。而孟子斥之以无父者也。今张子乃有此爱必兼爱之训。何也。曰。兼爱之言虽同。而兼爱之实。则不同。墨氏之兼爱。视路人如其亲。是为二本也。张子所谓爱必兼爱者。谓推吾爱亲之心而爱人之亲。推吾爱子之心而爱人之子也。是则大学明明德新民。中庸成己成物之道也。
问。一故神之义未详。曰。一故神者。谓神之所以为神者。以一而不二故也。是乃所以释阴阳不测之谓神也。故横渠自注云。两在故不测。问。此神字与鬼神之神。同否。曰。神则一也。谓之鬼神者。以神带阴阳之气者而言之也。单言神者。以其能管摄动静而不离乎阴阳之气者而言也。故朱子释程子语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黄勉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则神在其中。析而言之。则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妙用也。
王鲁斋造化论劄疑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者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而未尝离。乃谓之混沌。混沌者。言万物相混沌。而未始相离也。混沌已分。乃开天地。天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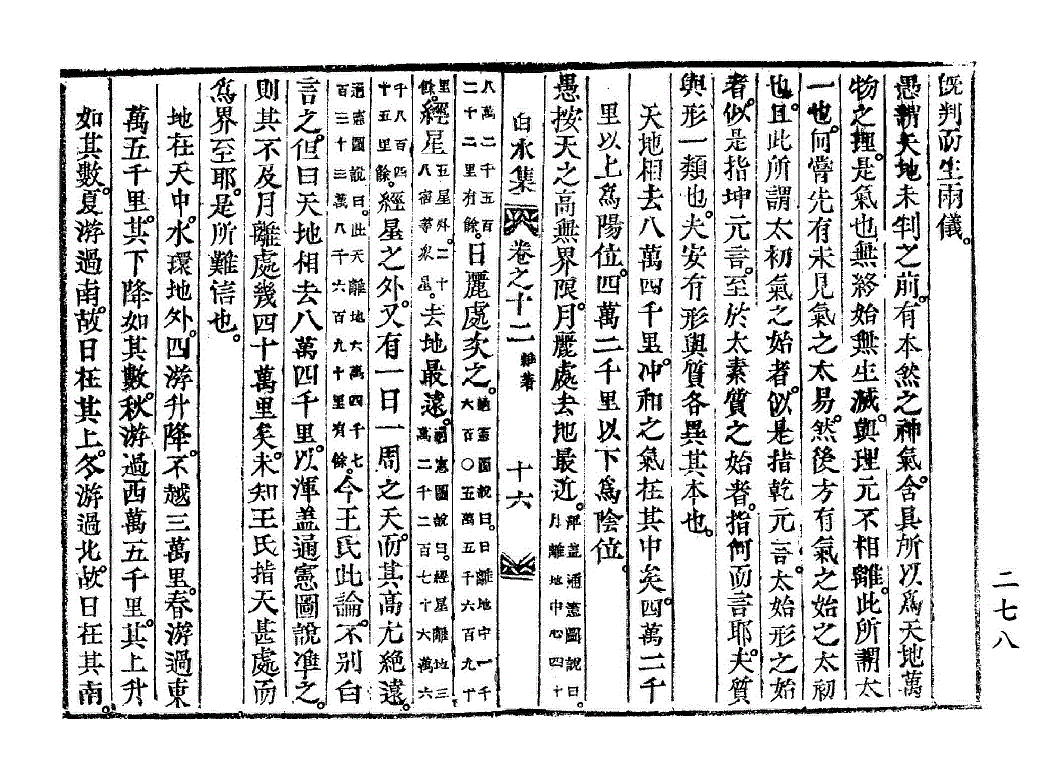 既判而生两仪。
既判而生两仪。愚谓天地未判之前。有本然之神气。含具所以为天地万物之理。是气也无终始无生灭。与理元不相离。此所谓太一也。何尝先有未见气之太易。然后方有气之始之太初也。且此所谓太初气之始者。似是指乾元言。太始形之始者。似是指坤元言。至于太素质之始者。指何而言耶。夫质与形一类也。夫安有形与质各异其本也。
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冲和之气在其中矣。四万二千里以上为阳位。四万二千里以下为阴位。
愚按天之高无界限。月丽处去地最近。(浑盖通宪图说曰。月离地中心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二十二里有馀。)日丽处次之。(通宪图说曰。日离地中一千六百〇五万五千六百九十里馀。)经星(五星外。二十八宿等众星。)去地最远。(通宪图说曰。经星离地三万二千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八百四十五里馀。)经星之外。又有一日一周之天。而其高尤绝远。(通宪图说曰。此天离地六万四千七百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九十里有馀。)今王氏此论。不别白言之。但曰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以浑盖通宪图说准之。则其不及月离处几四十万里矣。未知王氏指天甚处而为界至耶。是所难信也。
地在天中。水环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万里。春游过东万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数。秋游过西万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数。夏游过南。故日在其上。冬游过北。故日在其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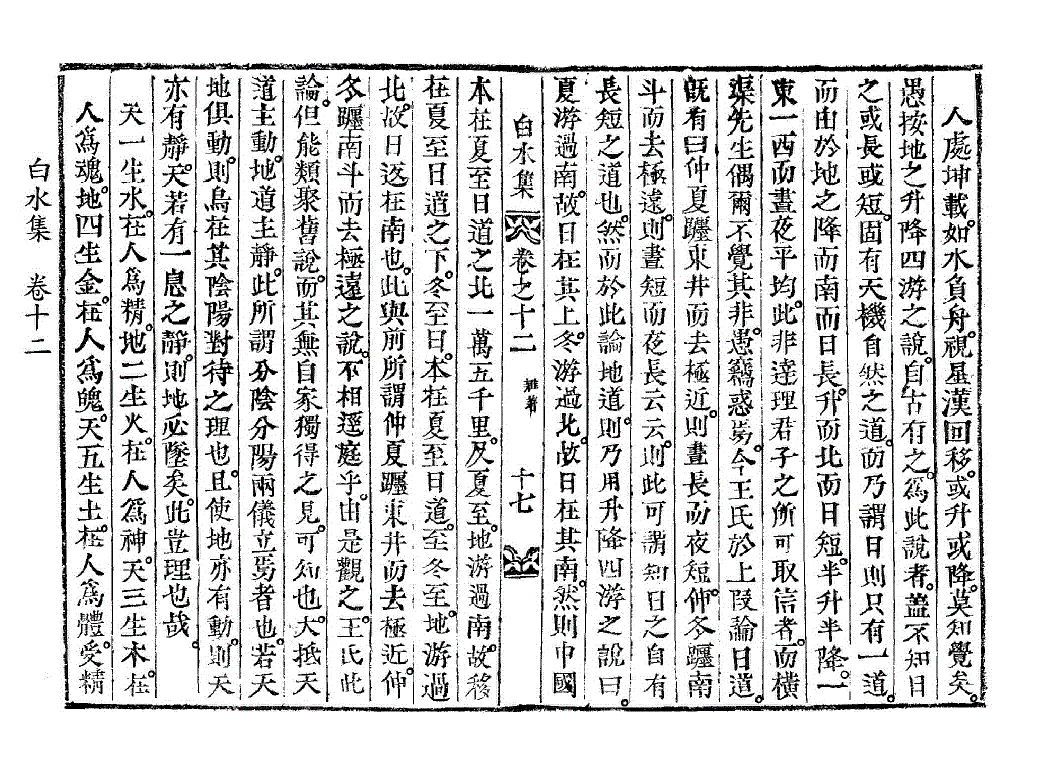 人处坤载。如水负舟。视星汉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觉矣。
人处坤载。如水负舟。视星汉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觉矣。愚按地之升降四游之说。自古有之。为此说者。盖不知日之或长或短。固有天机自然之道。而乃谓日则只有一道。而由于地之降而南而日长。升而北而日短。半升半降。一东一西而昼夜平均。此非达理君子之所可取信者。而横渠先生偶尔不觉其非。愚窃惑焉。今王氏于上段论日道。既有曰仲夏躔东井而去极近。则昼长而夜短。仲冬躔南斗而去极远。则昼短而夜长云云。则此可谓知日之自有长短之道也。然而于此论地道。则乃用升降四游之说曰。夏游过南。故日在其上。冬游过北。故日在其南。然则中国本在夏至日道之北一万五千里。及夏至。地游过南。故移在夏至日道之下。冬至日。本在夏至日道。至冬至。地游过北。故日返在南也。此与前所谓仲夏躔东井而去极近。仲冬躔南斗而去极远之说。不相径庭乎。由是观之。王氏此论。但能类聚旧说。而其无自家独得之见。可知也。大抵天道主动。地道主静。此所谓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若天地俱动。则乌在其阴阳对待之理也。且使地亦有动。则天亦有静。天若有一息之静。则地必坠矣。此岂理也哉。
天一生水。在人为精。地二生火。在人为神。天三生木。在人为魂。地四生金。在人为魄。天五生土。在人为体。受精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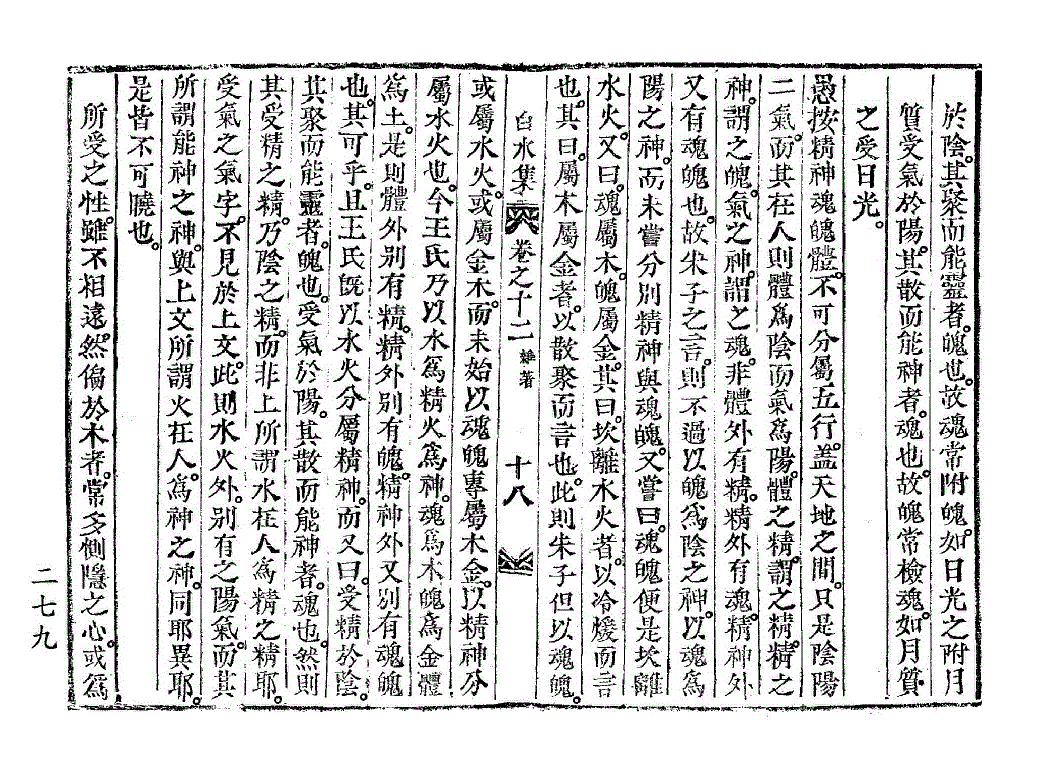 于阴。其聚而能灵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附月质受气于阳。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检魂。如月质之受日光。
于阴。其聚而能灵者。魄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附月质受气于阳。其散而能神者。魂也。故魄常检魂。如月质之受日光。愚按精神魂魄体。不可分属五行。盖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二气。而其在人则体为阴而气为阳。体之精。谓之精。精之神。谓之魄。气之神。谓之魂。非体外有精。精外有魂。精神外又有魂魄也。故朱子之言。则不过以魄为阴之神。以魂为阳之神。而未尝分别精神与魂魄。又尝曰。魂魄便是坎离水火。又曰。魂属木。魄属金。其曰。坎离水火者。以冷煖而言也。其曰。属木属金者。以散聚而言也。此则朱子但以魂魄。或属水火。或属金木。而未始以魂魄专属木金。以精神分属水火也。今王氏乃以水为精火为神。魂为木魄为金体为土。是则体外别有精。精外别有魄。精神外又别有魂魄也。其可乎。且王氏既以水火分属精神。而又曰。受精于阴。其聚而能灵者。魄也。受气于阳。其散而能神者。魂也。然则其受精之精。乃阴之精。而非上所谓水在人为精之精耶。受气之气字。不见于上文。此则水火外。别有之阳气。而其所谓能神之神。与上文所谓火在人。为神之神。同耶异耶。是皆不可晓也。
所受之性。虽不相远。然偏于木者。常多恻隐之心。或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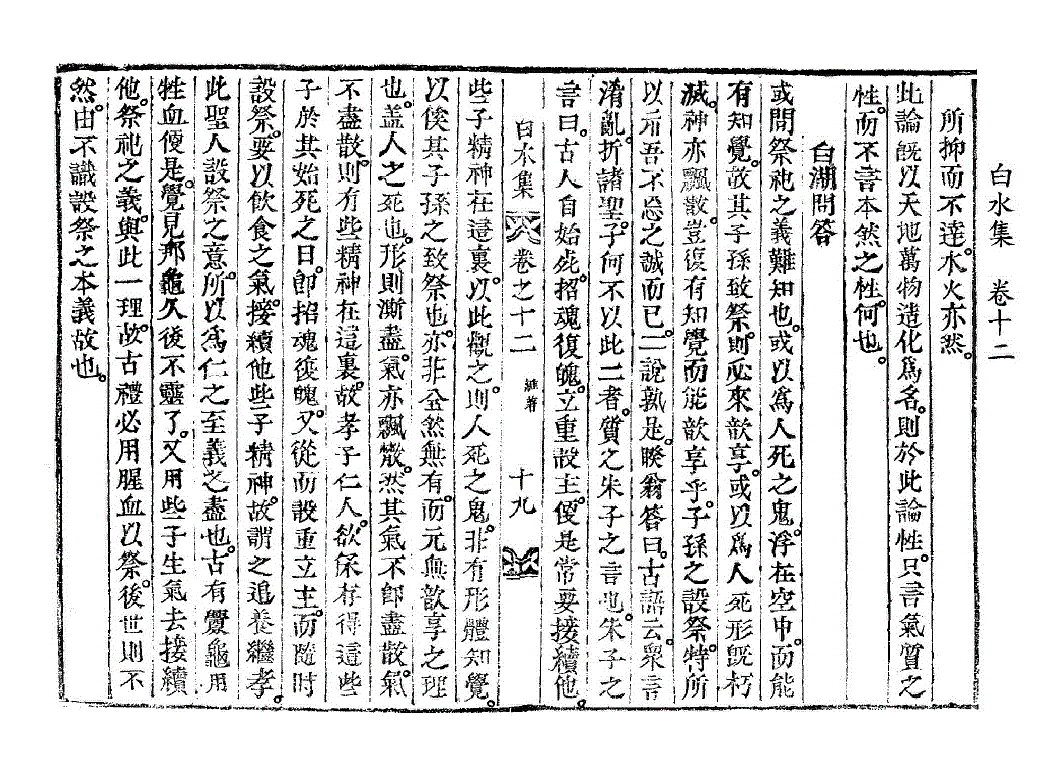 所抑而不达。水火亦然。
所抑而不达。水火亦然。此论既以天地万物造化为名。则于此论性。只言气质之性。而不言本然之性。何也。
白湖问答
或问祭祀之义难知也。或以为人死之鬼。浮在空中。而能有知觉。故其子孙致祭。则必来歆享。或以为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岂复有知觉而能歆享乎。子孙之设祭。特所以示吾不忘之诚而已。二说孰是。睽翁答曰。古语云。众言淆乱。折诸圣。子何不以此二者。质之朱子之言也。朱子之言曰。古人自始死。招魂复魄。立重设主。便是常要接续他。些子精神在这里。以此观之。则人死之鬼。非有形体知觉。以俟其子孙之致祭也。亦非全然无有。而元无歆享之理也。盖人之死也。形则澌尽。气亦飘散。然其气不即尽散。气不尽散。则有些精神在这里。故孝子仁人。欲保存得这些子于其始死之日。即招魂复魄。又从而设重立主。而随时设祭。要以饮食之气。接续他些子精神。故谓之追养继孝。此圣人设祭之意。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古有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祭祀之义。与此一理。故古礼必用腥血以祭。后世则不然。由不识设祭之本义故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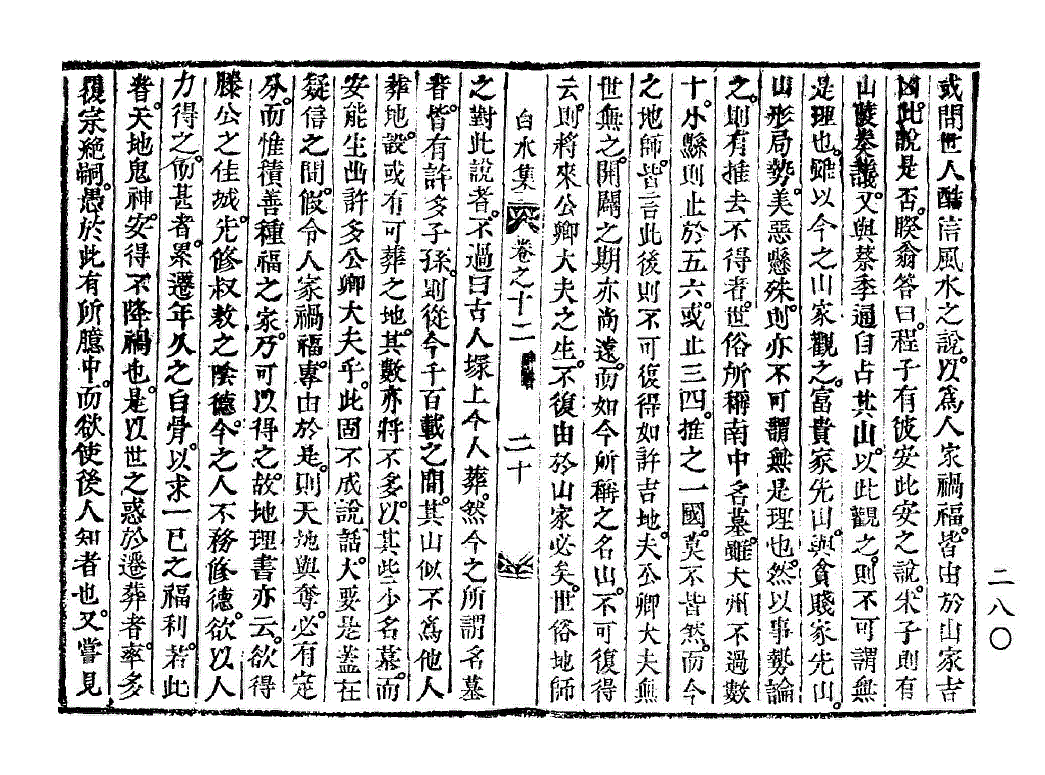 或问世人酷信风水之说。以为人家祸福。皆由于山家吉凶。此说是否。睽翁答曰。程子有彼安此安之说。朱子则有山陵奏议。又与蔡季通自占其山。以此观之。则不可谓无是理也。虽以今之山家观之。富贵家先山。与贫贱家先山。山形局势。美恶悬殊。则亦不可谓无是理也。然以事势论之。则有推去不得者。世俗所称南中名墓。虽大州不过数十。小县则止于五六。或止三四。推之一国。莫不皆然。而今之地师。皆言此后则不可复得如许吉地。夫公卿大夫无世无之。开辟之期亦尚远。而如今所称之名山。不可复得云。则将来公卿大夫之生。不复由于山家必矣。世俗地师之对此说者。不过曰古人冢上今人葬。然今之所谓名墓者。皆有许多子孙。则从今千百载之间。其山似不为他人葬地。设或有可葬之地。其数亦将不多。以其些少名墓。而安能生出许多公卿大夫乎。此固不成说话。大要是盖在疑信之间。假令人家祸福。专由于是。则天地与夺。必有定分。而惟积善种福之家。乃可以得之。故地理书亦云。欲得滕公之佳城。先修叔敖之阴德。今之人不务修德。欲以人力得之。而甚者。累迁年久之白骨。以求一己之福利。若此者。天地鬼神。安得不降祸也。是以世之惑于迁葬者。率多覆宗绝嗣。愚于此有所臆中。而欲使后人知者也。又尝见
或问世人酷信风水之说。以为人家祸福。皆由于山家吉凶。此说是否。睽翁答曰。程子有彼安此安之说。朱子则有山陵奏议。又与蔡季通自占其山。以此观之。则不可谓无是理也。虽以今之山家观之。富贵家先山。与贫贱家先山。山形局势。美恶悬殊。则亦不可谓无是理也。然以事势论之。则有推去不得者。世俗所称南中名墓。虽大州不过数十。小县则止于五六。或止三四。推之一国。莫不皆然。而今之地师。皆言此后则不可复得如许吉地。夫公卿大夫无世无之。开辟之期亦尚远。而如今所称之名山。不可复得云。则将来公卿大夫之生。不复由于山家必矣。世俗地师之对此说者。不过曰古人冢上今人葬。然今之所谓名墓者。皆有许多子孙。则从今千百载之间。其山似不为他人葬地。设或有可葬之地。其数亦将不多。以其些少名墓。而安能生出许多公卿大夫乎。此固不成说话。大要是盖在疑信之间。假令人家祸福。专由于是。则天地与夺。必有定分。而惟积善种福之家。乃可以得之。故地理书亦云。欲得滕公之佳城。先修叔敖之阴德。今之人不务修德。欲以人力得之。而甚者。累迁年久之白骨。以求一己之福利。若此者。天地鬼神。安得不降祸也。是以世之惑于迁葬者。率多覆宗绝嗣。愚于此有所臆中。而欲使后人知者也。又尝见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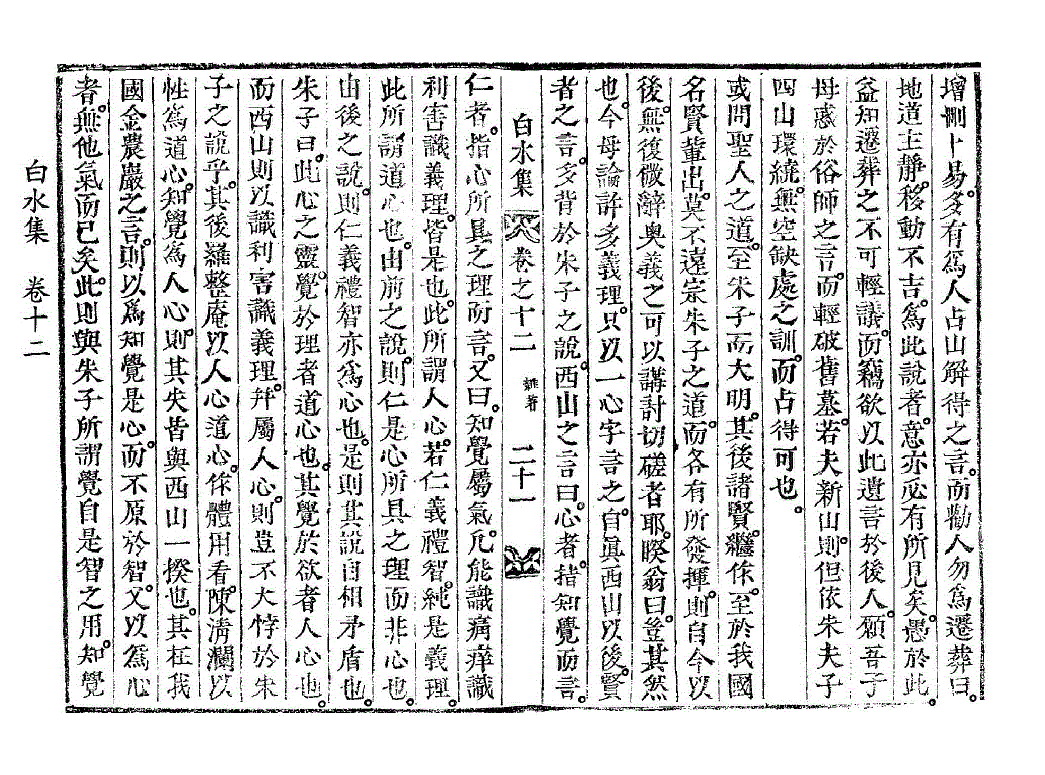 增删卜易。多有为人占山解得之言。而劝人勿为迁葬曰。地道主静。移动不吉。为此说者。意亦必有所见矣。愚于此。益知迁葬之不可轻议。而窃欲以此遗言于后人。愿吾子毋惑于俗师之言。而轻破旧墓。若夫新山。则但依朱夫子四山环绕。无空缺处之训。而占得可也。
增删卜易。多有为人占山解得之言。而劝人勿为迁葬曰。地道主静。移动不吉。为此说者。意亦必有所见矣。愚于此。益知迁葬之不可轻议。而窃欲以此遗言于后人。愿吾子毋惑于俗师之言。而轻破旧墓。若夫新山。则但依朱夫子四山环绕。无空缺处之训。而占得可也。或问圣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后诸贤。继作。至于我国名贤辈出。莫不远宗朱子之道。而各有所发挥。则自今以后。无复微辞奥义之可以讲讨切磋者耶。睽翁曰。岂其然也。今毋论许多义理。只以一心字言之。自真西山以后。贤者之言。多背于朱子之说。西山之言曰。心者。指知觉而言。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又曰。知觉属气。凡能识痛痒识利害识义理。皆是也。此所谓人心。若仁义礼智。纯是义理。此所谓道心也。由前之说。则仁是心所具之理而非心也。由后之说。则仁义礼智亦为心也。是则其说自相矛盾也。朱子曰。此心之灵。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而西山则以识利害识义理。并属人心。则岂不大悖于朱子之说乎。其后罗整庵以人心道心。作体用看。陈清澜以性为道心。知觉为人心。则其失皆与西山一揆也。其在我国金农岩之言。则以为知觉是心。而不原于智。又以为心者。无他气而已矣。此则与朱子所谓觉自是智之用。知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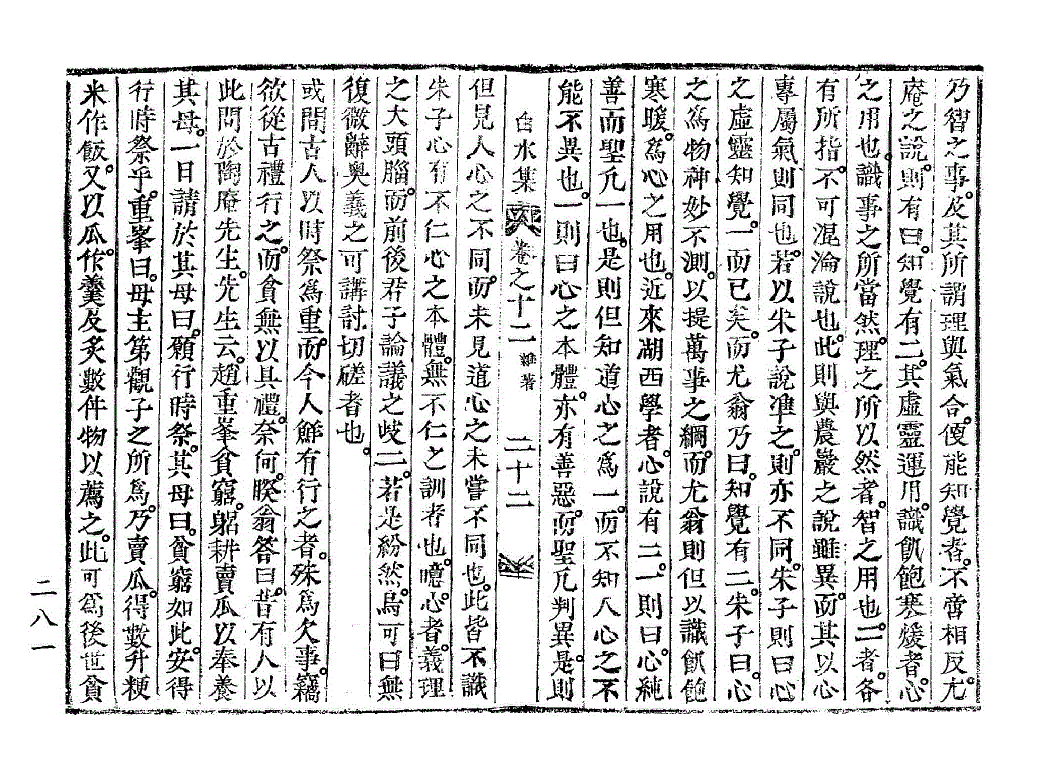 乃智之事。及其所谓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不啻相反。尤庵之说。则有曰。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识饥饱寒煖者。心之用也。识事之所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此则与农岩之说虽异。而其以心专属气则同也。若以朱子说准之。则亦不同。朱子则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尤翁乃曰。知觉有二。朱子曰。心之为物神妙不测。以提万事之纲。而尤翁则但以识饥饱寒暖。为心之用也。近来湖西学者。心说有二。一则曰。心纯善而圣凡一也。是则但知道心之为一。而不知人心之不能不异也。一则曰心之本体。亦有善恶。而圣凡判异。是则但见人心之不同。而未见道心之未尝不同也。此皆不识朱子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之训者也。噫。心者。义理之大头脑。而前后君子论议之歧二。若是纷然。乌可曰无复微辞奥义之可讲讨切磋者也。
乃智之事。及其所谓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不啻相反。尤庵之说。则有曰。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识饥饱寒煖者。心之用也。识事之所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此则与农岩之说虽异。而其以心专属气则同也。若以朱子说准之。则亦不同。朱子则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尤翁乃曰。知觉有二。朱子曰。心之为物神妙不测。以提万事之纲。而尤翁则但以识饥饱寒暖。为心之用也。近来湖西学者。心说有二。一则曰。心纯善而圣凡一也。是则但知道心之为一。而不知人心之不能不异也。一则曰心之本体。亦有善恶。而圣凡判异。是则但见人心之不同。而未见道心之未尝不同也。此皆不识朱子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之训者也。噫。心者。义理之大头脑。而前后君子论议之歧二。若是纷然。乌可曰无复微辞奥义之可讲讨切磋者也。或问古人以时祭为重。而今人鲜有行之者。殊为欠事。窃欲从古礼行之。而贫无以具礼。奈何。睽翁答曰。昔有人以此问于陶庵先生。先生云。赵重峰贫穷。躬耕卖瓜以奉养其母。一日请于其母曰。愿行时祭。其母曰。贫穷如此。安得行时祭乎。重峰曰。母主第观子之所为。乃卖瓜。得数升粳米作饭。又以瓜。作羹及炙数件物以荐之。此可为后世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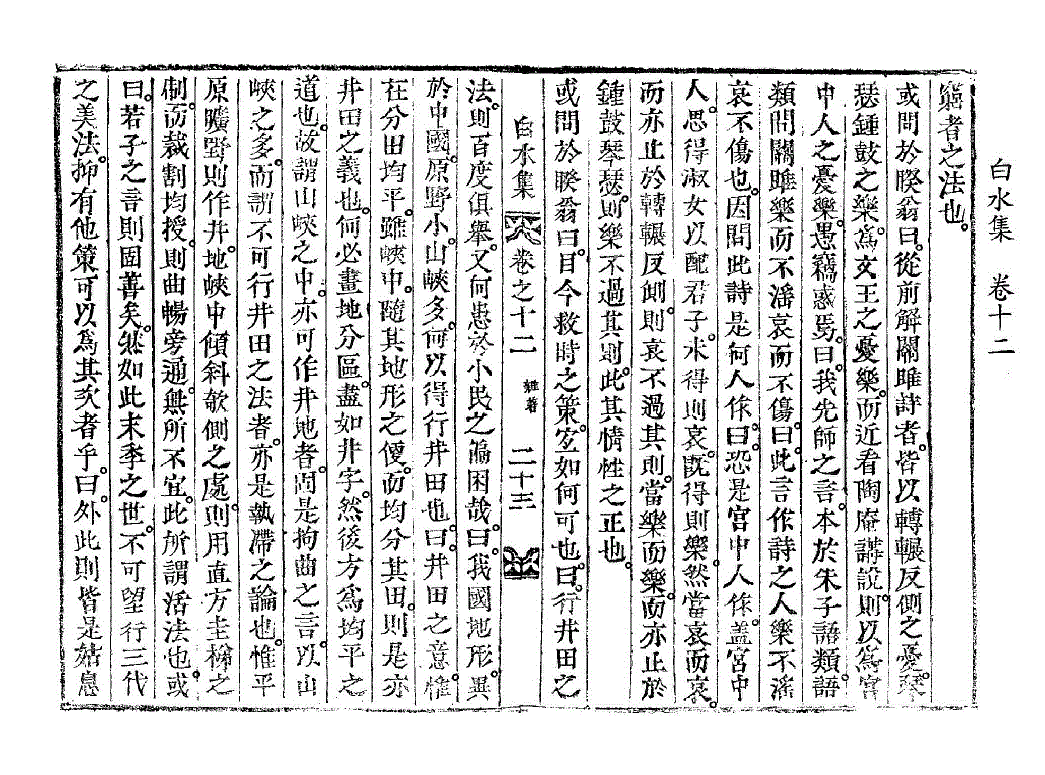 穷者之法也。
穷者之法也。或问于睽翁曰。从前解关雎诗者。皆以转辗反侧之忧。琴瑟钟鼓之乐。为文王之忧乐。而近看陶庵讲说。则以为宫中人之忧乐。愚窃惑焉。曰。我先师之言。本于朱子语类。语类问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曰。此言作诗之人乐不淫哀不伤也。因问此诗是何人作。曰。恐是宫中人作。盖宫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则哀。既得则乐。然当哀而哀。而亦止于转辗反侧。则哀不过其则。当乐而乐。而亦止于钟鼓琴瑟。则乐不过其则。此其情性之正也。
或问于睽翁曰。目今救时之策。宜如何可也。曰。行井田之法。则百度俱举。又何患于小民之偏困哉。曰。我国地形。异于中国。原野小。山峡多。何以得行井田也。曰。井田之意。惟在分田均平。虽峡中。随其地形之便。而均分其田。则是亦井田之义也。何必画地分区。尽如井字。然后方为均平之道也。故谓山峡之中。亦可作井地者。固是拘曲之言。以山峡之多。而谓不可行井田之法者。亦是执滞之论也。惟平原旷野则作井。地峡中倾斜欹侧之处。则用直方圭梯之制。而裁割均授。则曲畅旁通。无所不宜。此所谓活法也。或曰。若子之言则固善矣。然如此末季之世。不可望行三代之美法。抑有他策可以为其次者乎。曰。外此则皆是姑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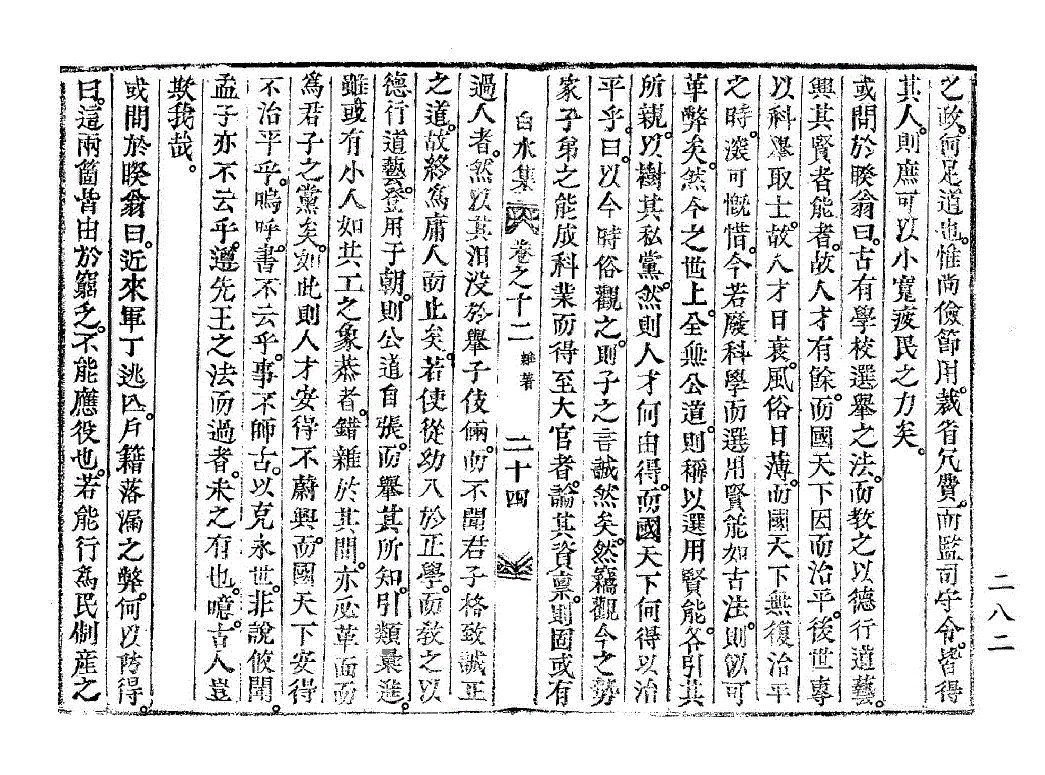 之政。何足道也。惟尚俭节用。裁省冗费。而监司守令。皆得其人。则庶可以小宽疲民之力矣。
之政。何足道也。惟尚俭节用。裁省冗费。而监司守令。皆得其人。则庶可以小宽疲民之力矣。或问于睽翁曰。古有学校选举之法。而教之以德行道艺。兴其贤者能者。故人才有馀。而国天下因而治平。后世专以科举取士。故人才日衰。风俗日薄。而国天下无复治平之时。深可慨惜。今若废科学而选用贤能如古法。则似可革弊矣。然今之世上。全无公道。则称以选用贤能。各引其所亲。以树其私党。然则人才何由得。而国天下何得以治平乎。曰。以今时俗观之。则子之言诚然矣。然窃观今之势家子弟之能成科业而得至大官者。论其资禀。则固或有过人者。然以其汩没于举子伎俩。而不闻君子格致诚正之道。故终为庸人而止矣。若使从幼入于正学。而教之以德行道艺。登用于朝。则公道自张。而举其所知。引类汇进。虽或有小人如共工之象恭者。错杂于其间。亦必革面而为君子之党矣。如此则人才安得不蔚兴。而国天下安得不治平乎。呜呼。书不云乎。事不师古。以克永世。非说攸闻。孟子亦不云乎。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噫。古人岂欺我哉。
或问于睽翁曰。近来军丁逃亡。户籍落漏之弊。何以防得。曰。这两个皆由于穷乏。不能应役也。若能行为民制产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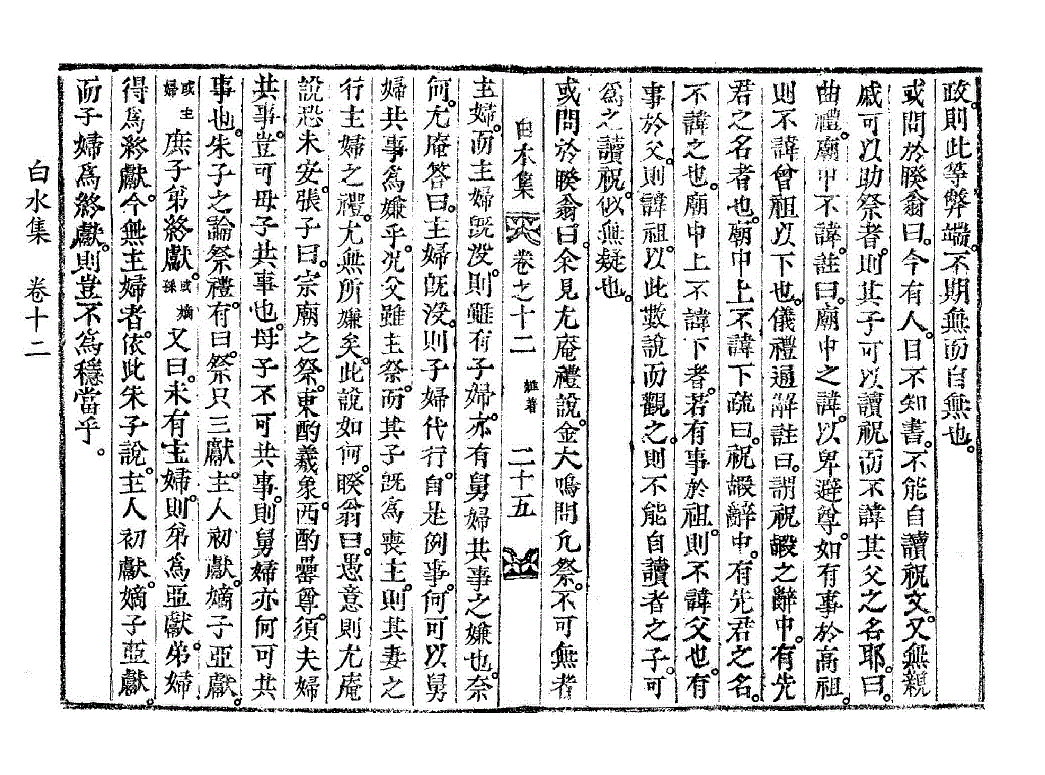 政。则此等弊端。不期无而自无也。
政。则此等弊端。不期无而自无也。或问于睽翁曰。今有人。目不知书。不能自读祝文。又无亲戚可以助祭者。则其子可以读祝而不讳其父之名耶。曰。曲礼。庙中不讳。注曰。庙中之讳。以卑避尊。如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也。仪礼通解注曰。谓祝嘏之辞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庙中上不讳下疏曰。祝嘏辞中。有先君之名。不讳之也。庙中上不讳下者。若有事于祖。则不讳父也。有事于父。则讳祖。以此数说而观之。则不能自读者之子。可为之读祝。似无疑也。
或问于睽翁曰。余见尤庵礼说。金大鸣问凡祭。不可无者主妇。而主妇既没。则虽有子妇。亦有舅妇共事之嫌也。奈何。尤庵答曰。主妇既没。则子妇代行。自是例事。何可以舅妇共事为嫌乎。况父虽主祭。而其子既为丧主。则其妻之行主妇之礼。尤无所嫌矣。此说如何。睽翁曰。愚意则尤庵说恐未安。张子曰。宗庙之祭。东酌羲象。西酌罍尊。须夫妇共事。岂可母子共事也。母子不可共事。则舅妇亦何可共事也。朱子之论祭礼。有曰。祭只三献。主人初献。嫡子亚献。(或主妇)庶子弟终献。(或嫡孙)又曰。未有主妇。则弟为亚献。弟妇得为终献。今无主妇者。依此朱子说。主人初献。嫡子亚献。而子妇为终献。则岂不为稳当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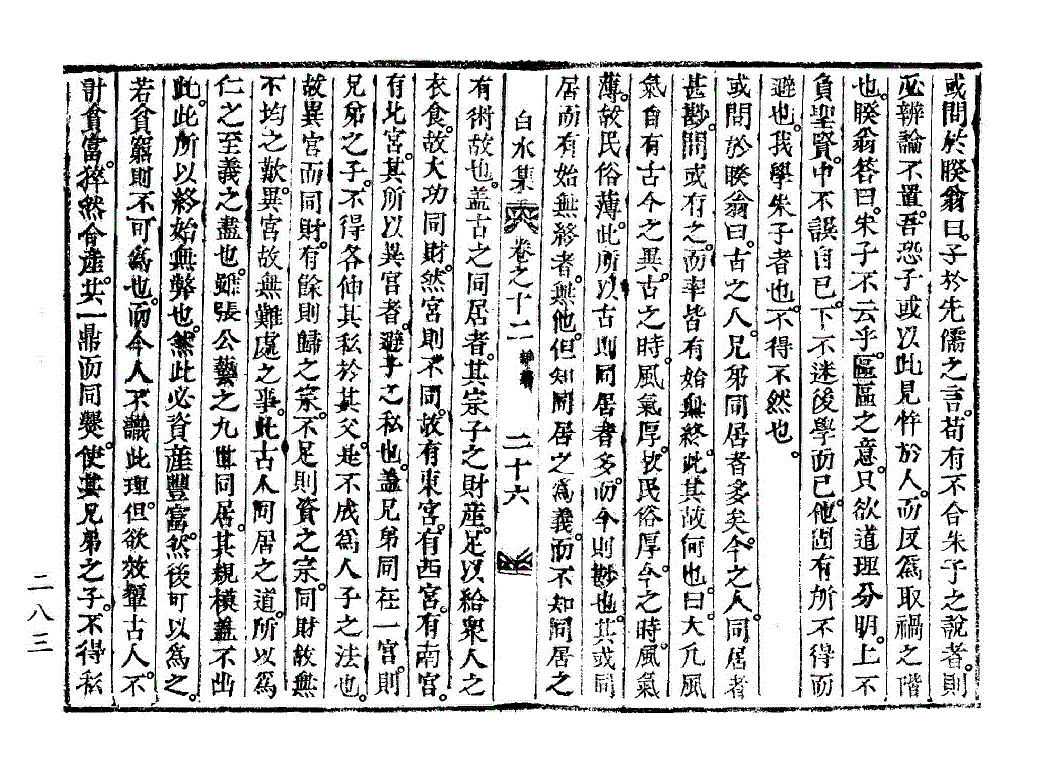 或问于睽翁曰。子于先儒之言。苟有不合朱子之说者。则必辨论不置。吾恐子或以此见忤于人。而反为取祸之阶也。睽翁答曰。朱子不云乎。区区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他固有所不得而避也。我学朱子者也。不得不然也。
或问于睽翁曰。子于先儒之言。苟有不合朱子之说者。则必辨论不置。吾恐子或以此见忤于人。而反为取祸之阶也。睽翁答曰。朱子不云乎。区区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他固有所不得而避也。我学朱子者也。不得不然也。或问于睽翁曰。古之人。兄弟同居者多矣。今之人。同居者甚鲜。间或有之。而率皆有始无终。此其故何也。曰。大凡风气自有古今之异。古之时。风气厚。故民俗厚。今之时。风气薄。故民俗薄。此所以古则同居者多。而今则鲜也。其或同居而有始无终者。无他。但知同居之为义。而不知同居之有术故也。盖古之同居者。其宗子之财产。足以给众人之衣食。故大功同财。然宫则不同。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其所以异宫者。避子之私也。盖兄弟同在一宫。则兄弟之子。不得各伸其私于其父。是不成为人子之法也。故异宫而同财。有馀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同财故无不均之叹。异宫故无难处之事。此古人同居之道。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虽张公艺之九世同居。其规模盖不出此。此所以终始无弊也。然此必资产丰富。然后可以为之。若贫穷则不可为也。而今人不识此理。但欲效颦古人。不计贫富。猝然合产。共一鼎而同爨。使其兄弟之子。不得私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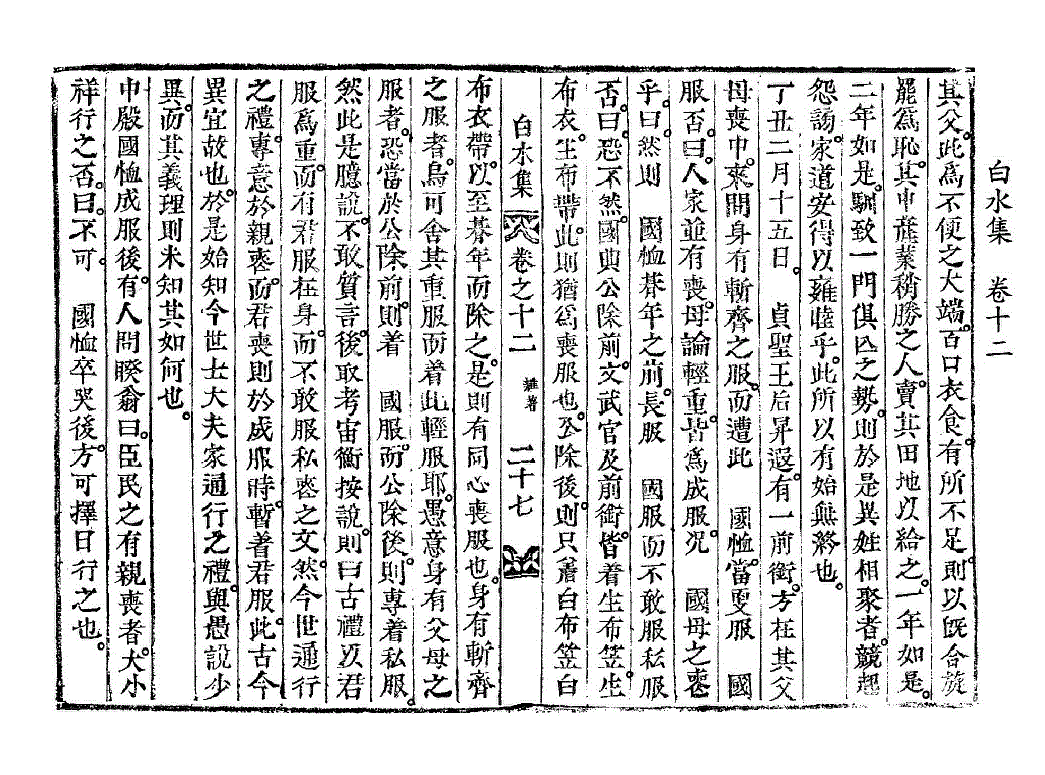 其父。此为不便之大端。百口衣食。有所不足。则以既合旋罢为耻。其中产业稍胜之人。卖其田地以给之。一年如是。二年如是。驯致一门俱亡之势。则于是异姓相聚者。竞起怨谤。家道安得以雍睦乎。此所以有始无终也。
其父。此为不便之大端。百口衣食。有所不足。则以既合旋罢为耻。其中产业稍胜之人。卖其田地以给之。一年如是。二年如是。驯致一门俱亡之势。则于是异姓相聚者。竞起怨谤。家道安得以雍睦乎。此所以有始无终也。丁丑二月十五日。 贞圣王后升遐。有一前衔。方在其父母丧中。来问身有斩齐之服。而遭此 国恤。当更服 国服否。曰。人家并有丧。毋论轻重。皆为成服。况 国母之丧乎。曰。然则 国恤期年之前。长服 国服而不敢服私服否。曰。恐不然。国典公除前。文武官及前衔。皆着生布笠。生布衣。生布带。此则犹为丧服也。公除后。则只着白布笠白布衣带。以至期年而除之。是则有同心丧服也。身有斩齐之服者。乌可舍其重服而着此轻服耶。愚意身有父母之服者。恐当于公除前。则着 国服。而公除后。则专着私服。然此是臆说。不敢质言。后取考宙衡按说。则曰古礼以君服为重。而有君服在身。而不敢服私丧之文。然今世通行之礼。专意于亲丧。而君丧则于成服时。暂着君服。此古今异宜故也。于是始知今世士大夫家通行之礼。与愚说少异。而其义理则未知其如何也。
中殿国恤成服后。有人问睽翁曰。臣民之有亲丧者。大小祥行之否。曰。不可。 国恤卒哭后。方可择日行之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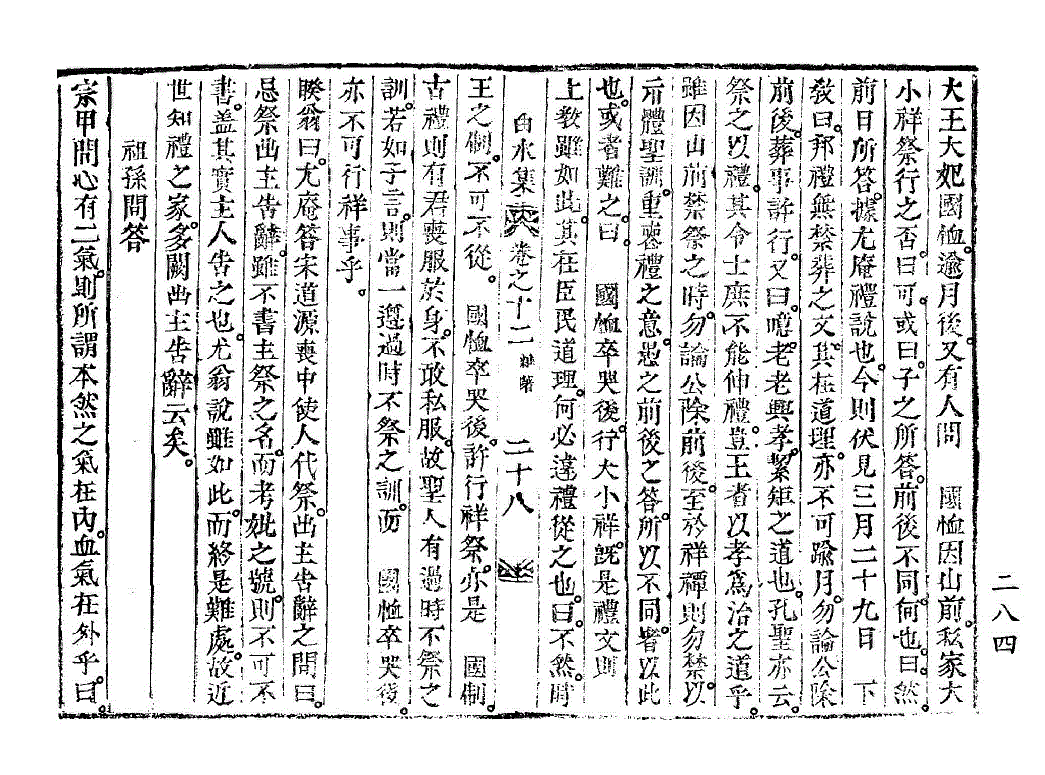 大王大妃国恤。逾月后。又有人问 国恤因山前。私家大小祥祭行之否。曰可。或曰。子之所答。前后不同。何也。曰。然。前日所答。据尤庵礼说也。今则伏见三月二十九日 下教曰。邦礼无禁葬之文。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勿论公除前后。葬事许行。又曰。噫。老老兴孝。絜矩之道也。孔圣亦云。祭之以礼。其令士庶不能伸礼。岂王者以孝为治之道乎。虽因山前禁祭之时。勿论公除前后。至于祥禫则勿禁。以示体圣训。重丧礼之意。愚之前后之答。所以不同。皆以此也。或者难之。曰。 国恤卒哭后。行大小祥。既是礼文则 上教虽如此。其在臣民道理。何必违礼从之也。曰。不然。时王之制。不可不从。 国恤卒哭后。许行祥祭。亦是 国制。古礼则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故圣人有过时不祭之训。若如子言。则当一遵过时不祭之训。而 国恤卒哭后。亦不可行祥事乎。
大王大妃国恤。逾月后。又有人问 国恤因山前。私家大小祥祭行之否。曰可。或曰。子之所答。前后不同。何也。曰。然。前日所答。据尤庵礼说也。今则伏见三月二十九日 下教曰。邦礼无禁葬之文。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勿论公除前后。葬事许行。又曰。噫。老老兴孝。絜矩之道也。孔圣亦云。祭之以礼。其令士庶不能伸礼。岂王者以孝为治之道乎。虽因山前禁祭之时。勿论公除前后。至于祥禫则勿禁。以示体圣训。重丧礼之意。愚之前后之答。所以不同。皆以此也。或者难之。曰。 国恤卒哭后。行大小祥。既是礼文则 上教虽如此。其在臣民道理。何必违礼从之也。曰。不然。时王之制。不可不从。 国恤卒哭后。许行祥祭。亦是 国制。古礼则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故圣人有过时不祭之训。若如子言。则当一遵过时不祭之训。而 国恤卒哭后。亦不可行祥事乎。睽翁曰。尤庵答宋道源丧中使人代祭。出主告辞之问曰。忌祭出主告辞。虽不书主祭之名。而考妣之号。则不可不书。盖其实主人告之也。尤翁说虽如此。而终是难处。故近世知礼之家。多阙出主告辞云矣。
祖孙问答
宗甲问心有二气。则所谓本然之气在内。血气在外乎。曰。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H 页
 然。然则二气虽妙合。而其中自有条理界分否。曰。然。此如理气之元不相离。而犹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混沦无别也。敢问何以知其然也。曰。以有形之物而推之。则无形之气。亦可知也。且就一身上言之。则皮中有肉。而皮肉之界分自别。肉中有骨。而肉骨之界分亦自别。骨中有髓。而骨髓之界分又自别。皮肉骨𩪷。只是一体。而四者之界分。各各有别如此者。以气之精粗。自有多少般数故也。有形之气之有条理界分如此。则无形之气。何独不然乎。是故。以一身中流行之气言之。则血为阴。气为阳。而血与气之界分自别。故医书曰。血为气配。注云。血譬则水也。气譬则风也。风行水上。有血气之象焉。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于此可见。气在内而为血之主。血在外而为气之配也。(医书说止此)气中亦有清浊之界分。故医书灵枢云。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荣在脉中。卫在脉外。又曰。荣气之行。自太阴始。至足厥阴终。一周于身也。详其一周于身。外至身体四肢。内至五脏六腑。无不周遍。故其五十周。无昼夜阴阳之殊。卫气之行。则不然。昼但周阳于身体四肢之外。不入五脏六腑之内。夜但周阴于五脏六腑之内。不出于身体四肢之外。故必五十周。至平朝。方与荣。大会于手太阴也。(灵枢说止此)血气荣卫。只是充体流行之一气。而其中气
然。然则二气虽妙合。而其中自有条理界分否。曰。然。此如理气之元不相离。而犹理自理气自气。不相混沦无别也。敢问何以知其然也。曰。以有形之物而推之。则无形之气。亦可知也。且就一身上言之。则皮中有肉。而皮肉之界分自别。肉中有骨。而肉骨之界分亦自别。骨中有髓。而骨髓之界分又自别。皮肉骨𩪷。只是一体。而四者之界分。各各有别如此者。以气之精粗。自有多少般数故也。有形之气之有条理界分如此。则无形之气。何独不然乎。是故。以一身中流行之气言之。则血为阴。气为阳。而血与气之界分自别。故医书曰。血为气配。注云。血譬则水也。气譬则风也。风行水上。有血气之象焉。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于此可见。气在内而为血之主。血在外而为气之配也。(医书说止此)气中亦有清浊之界分。故医书灵枢云。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荣在脉中。卫在脉外。又曰。荣气之行。自太阴始。至足厥阴终。一周于身也。详其一周于身。外至身体四肢。内至五脏六腑。无不周遍。故其五十周。无昼夜阴阳之殊。卫气之行。则不然。昼但周阳于身体四肢之外。不入五脏六腑之内。夜但周阴于五脏六腑之内。不出于身体四肢之外。故必五十周。至平朝。方与荣。大会于手太阴也。(灵枢说止此)血气荣卫。只是充体流行之一气。而其中气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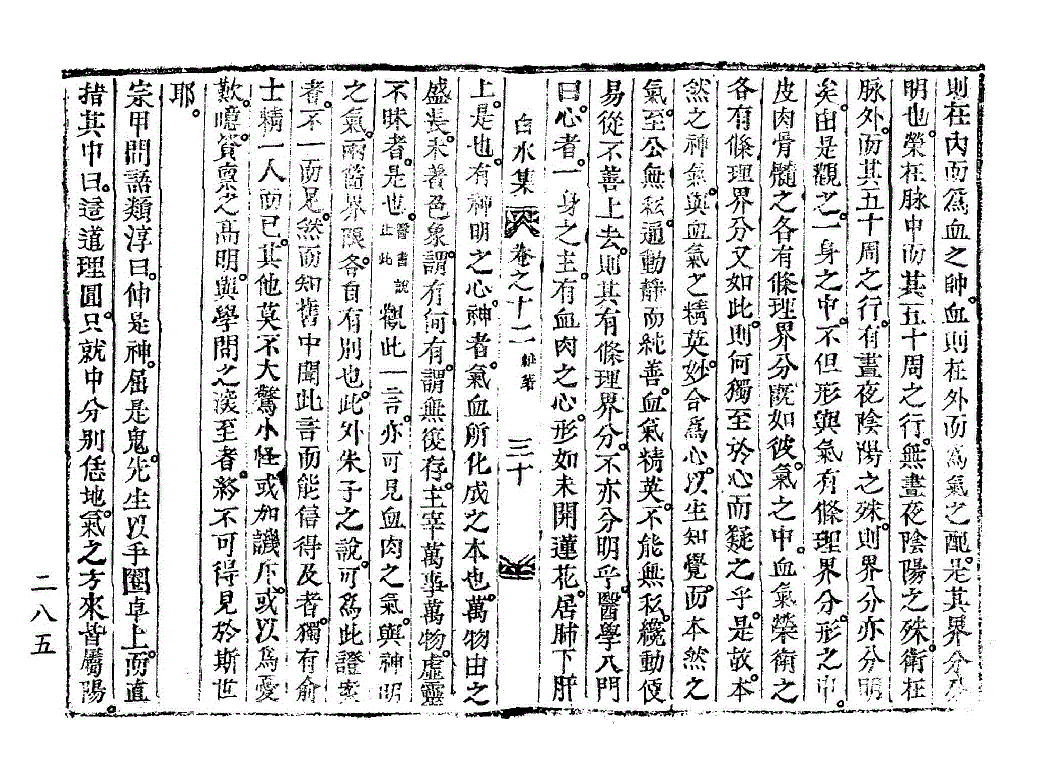 则在内而为血之帅。血则在外而为气之配。是其界分分明也。荣在脉中而其五十周之行。无昼夜阴阳之殊。卫在脉外。而其五十周之行。有昼夜阴阳之殊。则界分亦分明矣。由是观之。一身之中。不但形与气有条理界分。形之中。皮肉骨髓之各有条理界分既如彼。气之中。血气荣卫之各有条理界分又如此。则何独至于心而疑之乎。是故。本然之神气。与血气之精英。妙合为心。以生知觉。而本然之气。至公无私。通动静而纯善。血气精英。不能无私。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则其有条理界分。不亦分明乎。医学入门曰。心者。一身之主。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成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未着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医书说止此)观此一言。亦可见血肉之气。与神明之气。两个界限。各自有别也。此外朱子之说。可为此證案者。不一而足。然而知旧中闻此言而能信得及者。独有俞士精一人而已。其他莫不大惊小怪或加讥斥。或以为忧叹。噫。资禀之高明。与学问之深至者。终不可得见于斯世耶。
则在内而为血之帅。血则在外而为气之配。是其界分分明也。荣在脉中而其五十周之行。无昼夜阴阳之殊。卫在脉外。而其五十周之行。有昼夜阴阳之殊。则界分亦分明矣。由是观之。一身之中。不但形与气有条理界分。形之中。皮肉骨髓之各有条理界分既如彼。气之中。血气荣卫之各有条理界分又如此。则何独至于心而疑之乎。是故。本然之神气。与血气之精英。妙合为心。以生知觉。而本然之气。至公无私。通动静而纯善。血气精英。不能无私。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则其有条理界分。不亦分明乎。医学入门曰。心者。一身之主。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成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未着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医书说止此)观此一言。亦可见血肉之气。与神明之气。两个界限。各自有别也。此外朱子之说。可为此證案者。不一而足。然而知旧中闻此言而能信得及者。独有俞士精一人而已。其他莫不大惊小怪或加讥斥。或以为忧叹。噫。资禀之高明。与学问之深至者。终不可得见于斯世耶。宗甲问语类淳曰。伸是神。屈是鬼。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这道理圆。只就中分别恁地。气之方来皆属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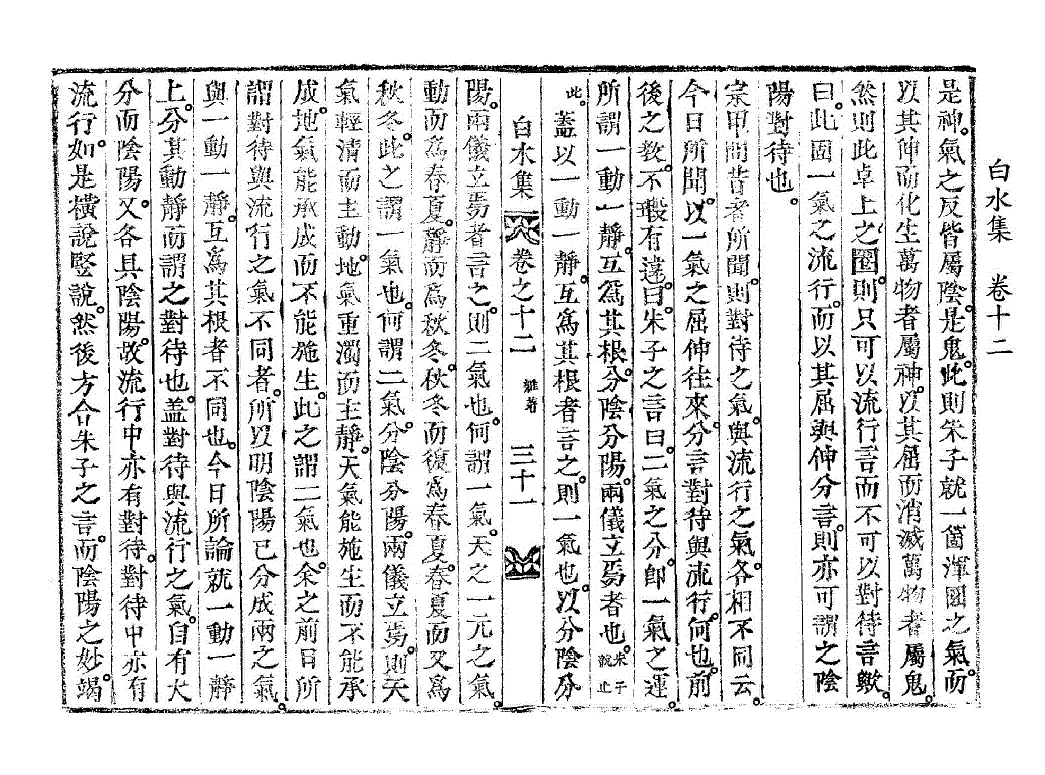 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此则朱子就一个浑圆之气。而以其伸而化生万物者属神。以其屈而消灭万物者属鬼。然则此卓上之圈。则只可以流行言而不可以对待言欤。曰。此固一气之流行。而以其屈与伸分言。则亦可谓之阴阳对待也。
是神。气之反皆属阴。是鬼。此则朱子就一个浑圆之气。而以其伸而化生万物者属神。以其屈而消灭万物者属鬼。然则此卓上之圈。则只可以流行言而不可以对待言欤。曰。此固一气之流行。而以其屈与伸分言。则亦可谓之阴阳对待也。宗甲问昔者所闻。则对待之气。与流行之气。各相不同云。今日所闻。以一气之屈伸往来。分言对待与流行。何也。前后之教。不瑕有违。曰。朱子之言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朱子说止此。)盖以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言之。则一气也。以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言之。则二气也。何谓一气。天之一元之气。动而为春夏。静而为秋冬。秋冬而复为春夏。春夏而又为秋冬。此之谓一气也。何谓二气。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则天气轻清而主动。地气重浊而主静。天气能施生而不能承成。地气能承成而不能施生。此之谓二气也。余之前日所谓对待与流行之气不同者。所以明阴阳已分成两之气。与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不同也。今日所论就一动一静上。分其动静而谓之对待也。盖对待与流行之气。自有大分而阴阳。又各具阴阳。故流行中亦有对待。对待中亦有流行。如是横说竖说。然后方合朱子之言。而阴阳之妙。竭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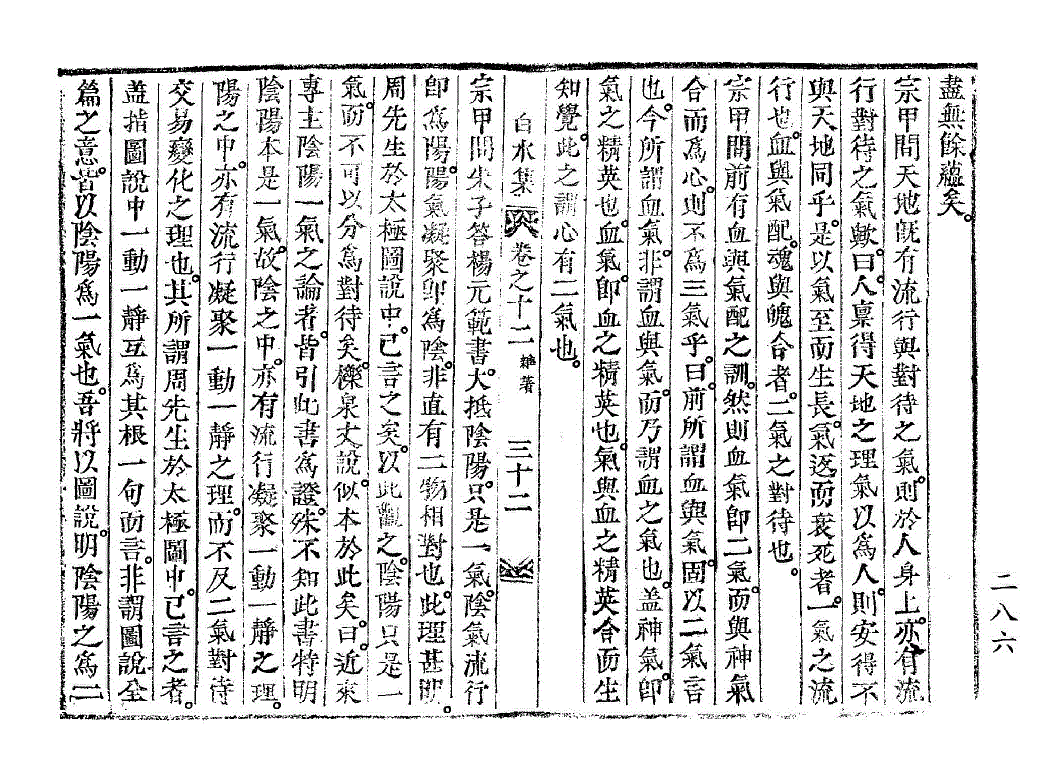 尽无馀蕴矣。
尽无馀蕴矣。宗甲问天地既有流行与对待之气。则于人身上。亦有流行对待之气欤。曰。人禀得天地之理气以为人。则安得不与天地同乎。是以气至而生长。气返而衰死者。一气之流行也。血与气配。魂与魄合者。二气之对待也。
宗甲问前有血与气配之训。然则血气即二气。而与神气合而为心。则不为三气乎。曰。前所谓血与气。固以二气言也。今所谓血气。非谓血与气。而乃谓血之气也。盖神气。即气之精英也。血气。即血之精英也。气与血之精英合而生知觉。此之谓心有二气也。
宗甲问朱子答杨元范书。大抵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非直有二物相对也。此理甚明。周先生于太极图说中。已言之矣。以此观之。阴阳只是一气。而不可以分为对待矣。栎泉丈说。似本于此矣。曰。近来专主阴阳一气之论者。皆引此书为證。殊不知此书特明阴阳本是一气。故阴之中。亦有流行凝聚一动一静之理。阳之中。亦有流行凝聚一动一静之理。而不及二气对待交易变化之理也。其所谓周先生于太极图中。已言之者。盖指图说中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一句而言。非谓图说全篇之意。皆以阴阳为一气也。吾将以图说。明阴阳之为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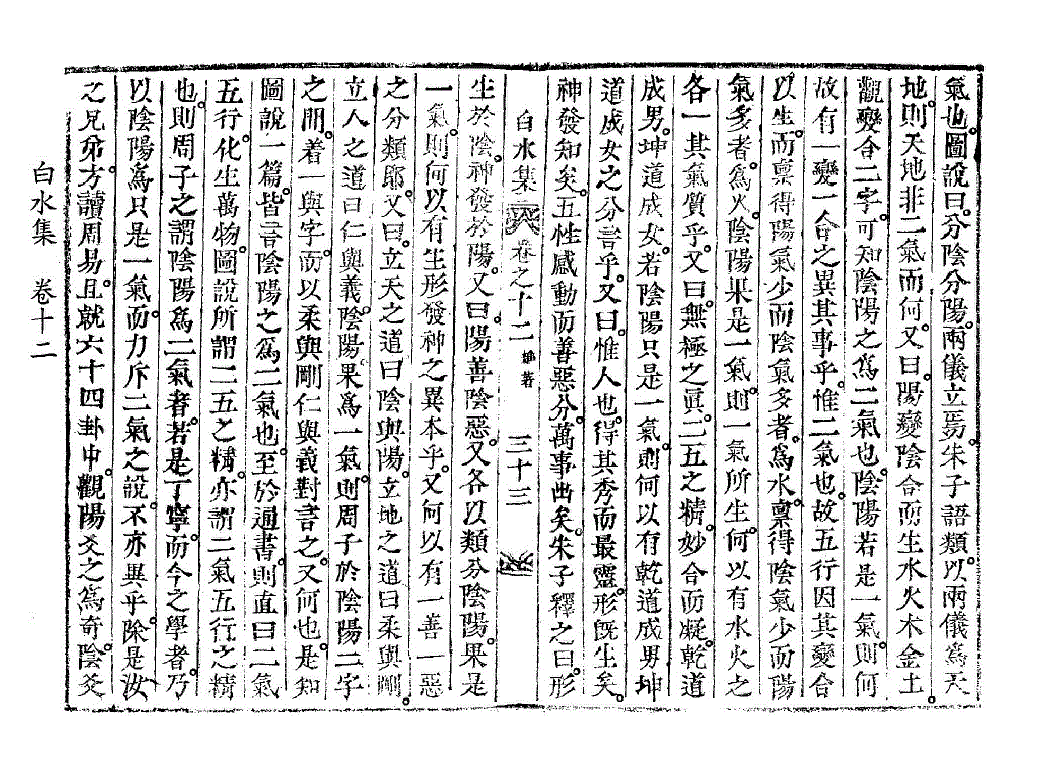 气也。图说曰。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语类。以两仪为天地。则天地非二气而何。又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观变合二字。可知阴阳之为二气也。阴阳若是一气。则何故有一变一合之异其事乎。惟二气也。故五行因其变合以生。而禀得阳气少而阴气多者。为水。禀得阴气少而阳气多者。为火。阴阳果是一气。则一气所生。何以有水火之各一其气质乎。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阴阳只是一气。则何以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分言乎。又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朱子释之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又曰。阳善阴恶。又各以类分阴阳。果是一气。则何以有生形发神之异本乎。又何以有一善一恶之分类耶。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果为一气。则周子于阴阳二字之间。着一与字。而以柔与刚仁与义对言之。又何也。是知图说一篇。皆言阴阳之为二气也。至于通书。则直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图说所谓二五之精。亦谓二气五行之精也。则周子之谓阴阳为二气者。若是丁宁。而今之学者。乃以阴阳为只是一气。而力斥二气之说。不亦异乎。除是汝之兄弟。方读周易。且就六十四卦中。观阳爻之为奇。阴爻
气也。图说曰。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朱子语类。以两仪为天地。则天地非二气而何。又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观变合二字。可知阴阳之为二气也。阴阳若是一气。则何故有一变一合之异其事乎。惟二气也。故五行因其变合以生。而禀得阳气少而阴气多者。为水。禀得阴气少而阳气多者。为火。阴阳果是一气。则一气所生。何以有水火之各一其气质乎。又曰。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若阴阳只是一气。则何以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分言乎。又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朱子释之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又曰。阳善阴恶。又各以类分阴阳。果是一气。则何以有生形发神之异本乎。又何以有一善一恶之分类耶。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果为一气。则周子于阴阳二字之间。着一与字。而以柔与刚仁与义对言之。又何也。是知图说一篇。皆言阴阳之为二气也。至于通书。则直曰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图说所谓二五之精。亦谓二气五行之精也。则周子之谓阴阳为二气者。若是丁宁。而今之学者。乃以阴阳为只是一气。而力斥二气之说。不亦异乎。除是汝之兄弟。方读周易。且就六十四卦中。观阳爻之为奇。阴爻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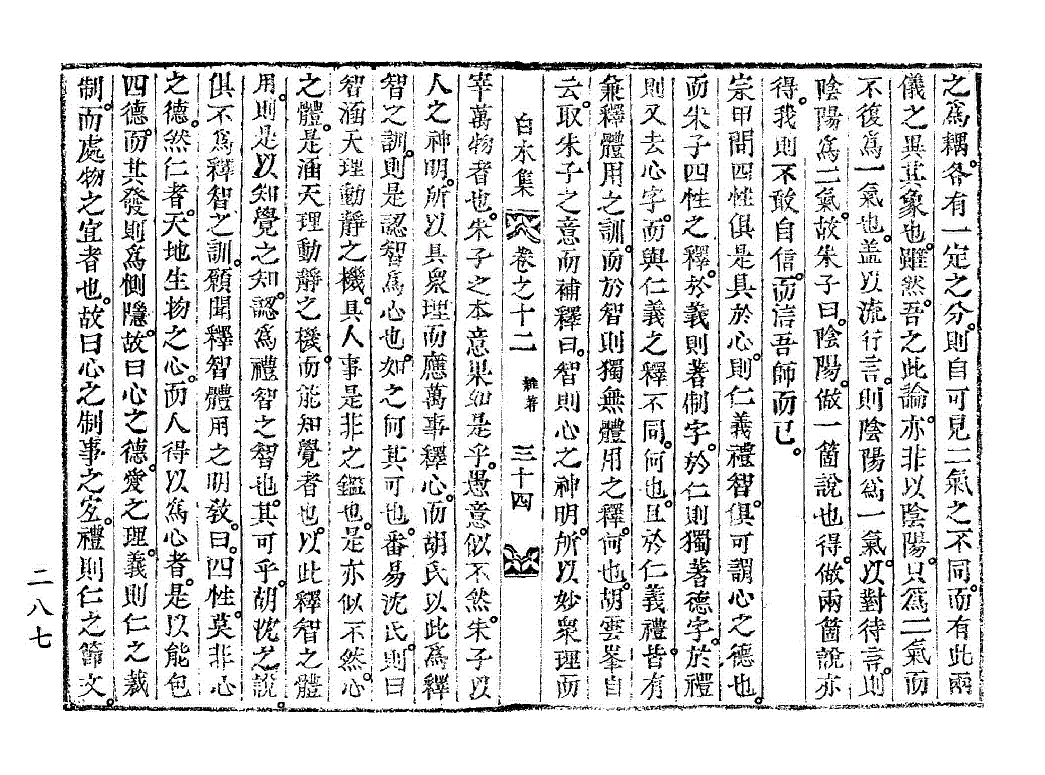 之为耦。各有一定之分。则自可见二气之不同。而有此两仪之异其象也。虽然。吾之此论。亦非以阴阳。只为二气而不复为一气也。盖以流行言。则阴阳为一气。以对待言。则阴阳为二气。故朱子曰。阴阳。做一个说也得。做两个说亦得。我则不敢自信。而信吾师而已。
之为耦。各有一定之分。则自可见二气之不同。而有此两仪之异其象也。虽然。吾之此论。亦非以阴阳。只为二气而不复为一气也。盖以流行言。则阴阳为一气。以对待言。则阴阳为二气。故朱子曰。阴阳。做一个说也得。做两个说亦得。我则不敢自信。而信吾师而已。宗甲问四性俱是具于心。则仁义礼智。俱可谓心之德也。而朱子四性之释。于义则著制字。于仁则独著德字。于礼则又去心字。而与仁义之释不同。何也。且于仁义礼。皆有兼释体用之训。而于智则独无体用之释。何也。胡云峰自云。取朱子之意而补释曰。智则心之神明。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朱子之本意果如是乎。愚意似不然。朱子以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释心。而胡氏以此为释智之训。则是认智为心也。如之何其可也。番易沈氏。则曰智涵天理动静之机。具人事是非之鉴也。是亦似不然。心之体。是涵天理动静之机。而能知觉者也。以此释智之体用。则是以知觉之知。认为礼智之智也。其可乎。胡沈之说。俱不为释智之训。愿闻释智体用之明教。曰。四性。莫非心之德。然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为心者。是以能包四德。而其发则为恻隐。故曰心之德。爱之理。义则仁之裁制。而处物之宜者也。故曰心之制事之宜。礼则仁之节文。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8H 页
 而著见乎外者也。故不复言心。而以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释之也。于智独无兼释体用之训。未知其何故也。然既有曰。智者。分别是非之理。又有曰。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合此两言观之。则智之体用。亦可见也。胡,沈释智之失。乃言得之。金农岩亦尝斥之。其言则是矣。但农岩以知觉为非智之用。则亦失朱子之意矣。释智体用之请。汝以余为贤于胡,沈而为此言耶。然余于此尝讲之熟矣。故敢依朱子释仁义之体例而立言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妙也。未知将不复有如农岩讥斥之者乎。
而著见乎外者也。故不复言心。而以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释之也。于智独无兼释体用之训。未知其何故也。然既有曰。智者。分别是非之理。又有曰。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合此两言观之。则智之体用。亦可见也。胡,沈释智之失。乃言得之。金农岩亦尝斥之。其言则是矣。但农岩以知觉为非智之用。则亦失朱子之意矣。释智体用之请。汝以余为贤于胡,沈而为此言耶。然余于此尝讲之熟矣。故敢依朱子释仁义之体例而立言曰智者知之理心之妙也。未知将不复有如农岩讥斥之者乎。宗甲问五行之神。在人为五性。而五行之性。各自不同。则朱子所谓仁包四性者。殊可疑也。且以五行相生之理言之。水生木则水为木之父也。仁何能统智乎。以其相克之理言之。金克木则金为木之敌也。义何为仁包乎。以此推之。仁包四性之说。不能无惑也。且仁若包礼义智乎。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俱是仁之用也。然则人能极其为仁之工。则义礼智亦自成熟。而似别无三者之工。此如纲举而目张矣。未知如何。曰。观五行之成质者。则自有相生相克之道。而论天地之大德。则只是生理而已。故盈天地之间者。莫不以生气为主本。以天道言之。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然春生之气。统得四时。而无拘于夏火秋金冬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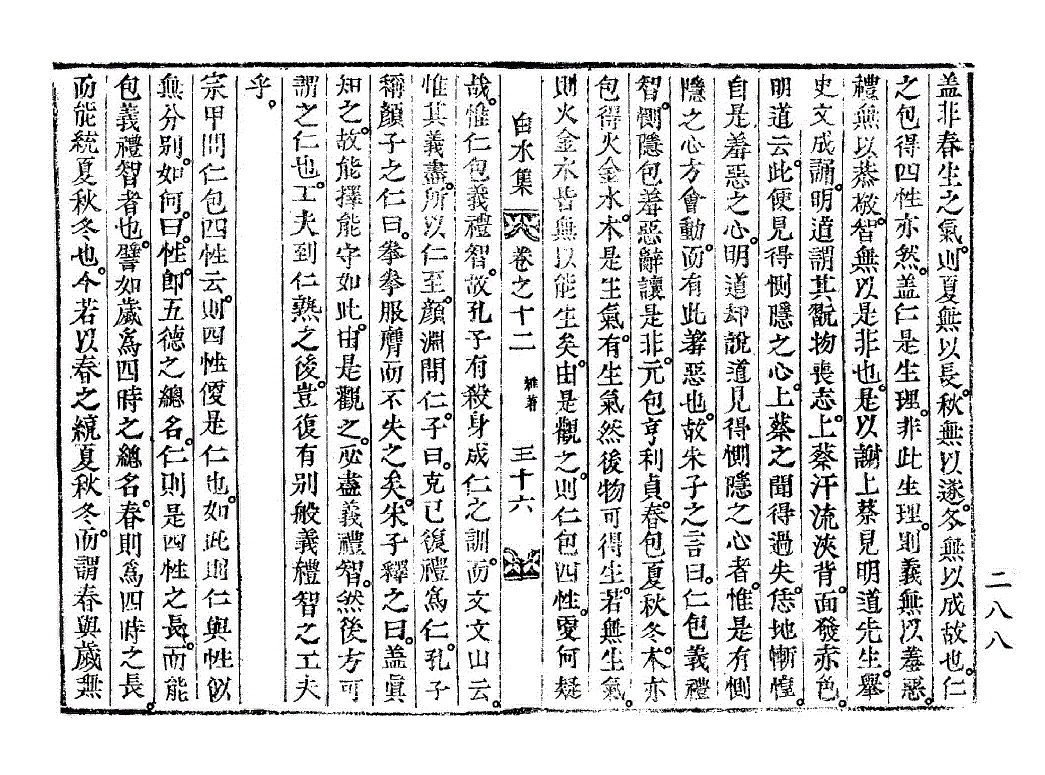 盖非春生之气。则夏无以长。秋无以遂。冬无以成故也。仁之包得四性亦然。盖仁是生理。非此生理。则义无以羞恶。礼无以恭敬。智无以是非也。是以谢上蔡见明道先生。举史文成诵。明道谓其玩物丧志。上蔡汗流浃背。面发赤色。明道云。此便见得恻隐之心。上蔡之闻得过失。恁地惭惶。自是羞恶之心。明道却说道见得恻隐之心者。惟是有恻隐之心方会动。而有此羞恶也。故朱子之言曰。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让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木亦包得火金水。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以能生矣。由是观之。则仁包四性。更何疑哉。惟仁包义礼智。故孔子有杀身成仁之训。而文文山云。惟其义尽。所以仁至。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称颜子之仁曰。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朱子释之曰。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由是观之。必尽义礼智。然后方可谓之仁也。工夫到仁熟之后。岂复有别般义礼智之工夫乎。
盖非春生之气。则夏无以长。秋无以遂。冬无以成故也。仁之包得四性亦然。盖仁是生理。非此生理。则义无以羞恶。礼无以恭敬。智无以是非也。是以谢上蔡见明道先生。举史文成诵。明道谓其玩物丧志。上蔡汗流浃背。面发赤色。明道云。此便见得恻隐之心。上蔡之闻得过失。恁地惭惶。自是羞恶之心。明道却说道见得恻隐之心者。惟是有恻隐之心方会动。而有此羞恶也。故朱子之言曰。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让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木亦包得火金水。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以能生矣。由是观之。则仁包四性。更何疑哉。惟仁包义礼智。故孔子有杀身成仁之训。而文文山云。惟其义尽。所以仁至。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称颜子之仁曰。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朱子释之曰。盖真知之。故能择能守如此。由是观之。必尽义礼智。然后方可谓之仁也。工夫到仁熟之后。岂复有别般义礼智之工夫乎。宗甲问仁包四性云。则四性便是仁也。如此则仁与性似无分别。如何。曰。性。即五德之总名。仁则是四性之长。而能包义礼智者也。譬如岁为四时之总名。春则为四时之长。而能统夏秋冬也。今若以春之统夏秋冬。而谓春与岁无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第 2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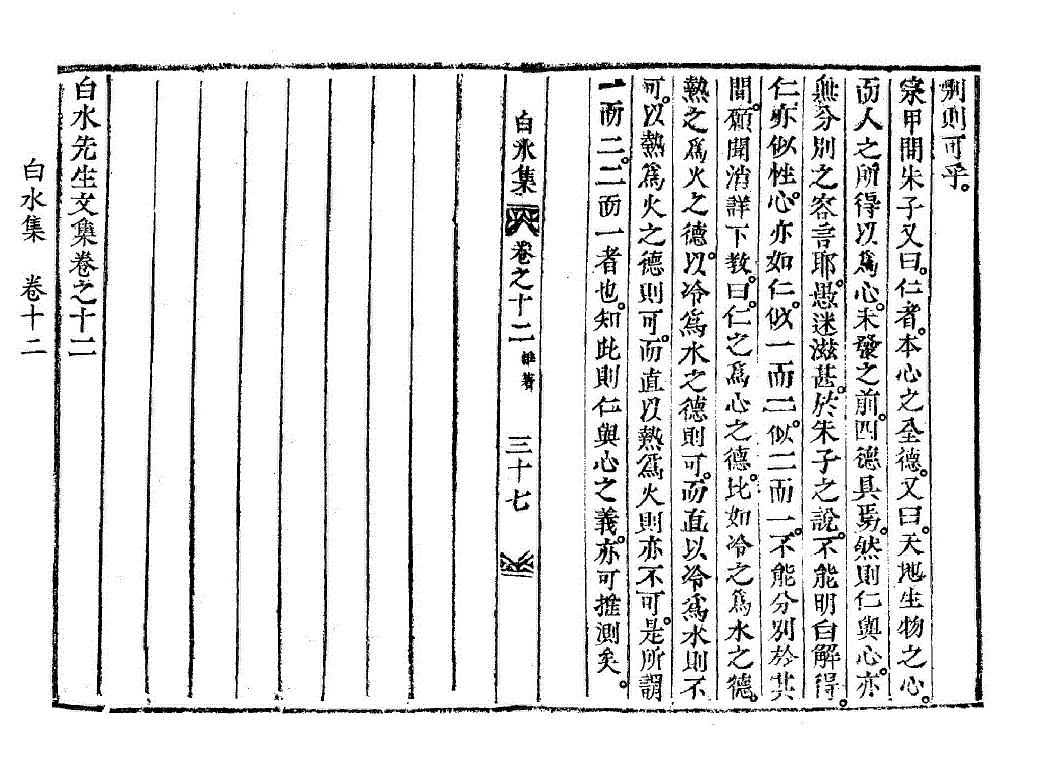 别则可乎。
别则可乎。宗甲问朱子又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又曰。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未发之前。四德具焉。然则仁与心。亦无分别之容言耶。愚迷滋甚。于朱子之说。不能明白解得。仁亦似性。心亦如仁。似一而二。似二而一。不能分别于其间。愿闻消详下教。曰。仁之为心之德。比如冷之为水之德。热之为火之德。以冷为水之德则可。而直以冷为水则不可。以热为火之德则可。而直以热为火则亦不可。是所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知此则仁与心之义。亦可推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