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杂著
杂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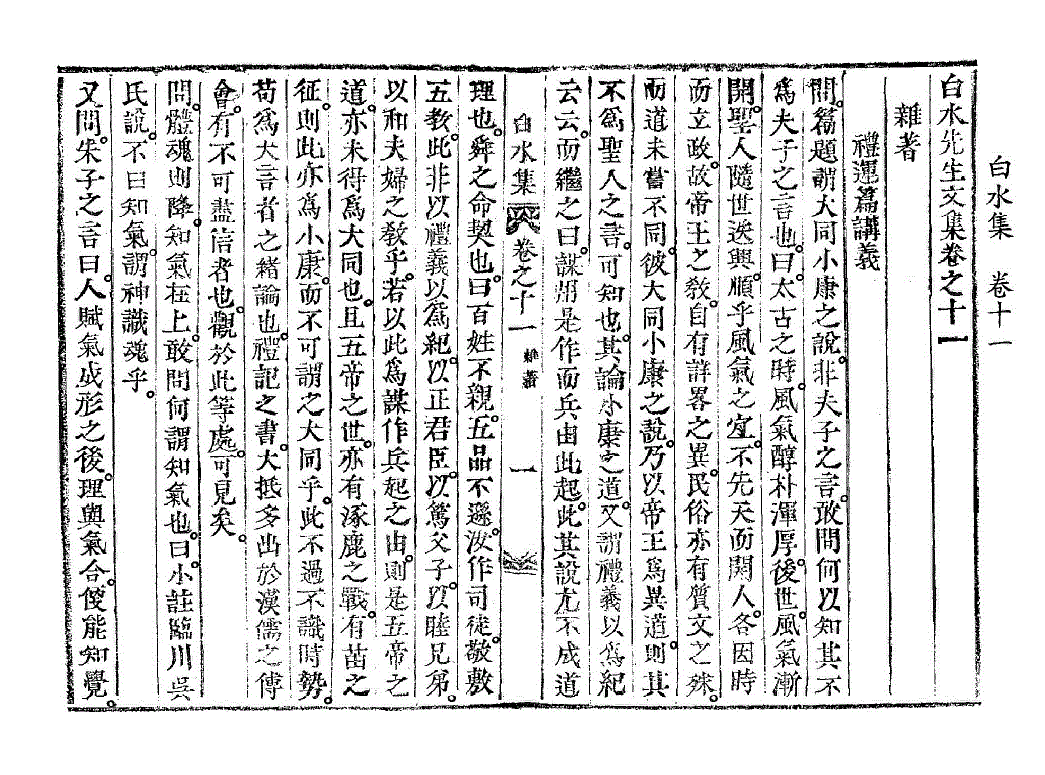 礼运篇讲义
礼运篇讲义问。篇题谓大同小康之说。非夫子之言。敢问何以知其不为夫子之言也。曰。太古之时。风气醇朴浑厚。后世。风气渐开。圣人随世迭兴。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而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故帝王之教。自有详略之异。民俗亦有质文之殊。而道未尝不同。彼大同小康之说。乃以帝王为异道。则其不为圣人之言。可知也。其论小康之道。又谓礼义以为纪云云。而继之曰。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此其说尤不成道理也。舜之命契也。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此非以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之教乎。若以此为谋作兵起之由。则是五帝之道。亦未得为大同也。且五帝之世。亦有涿鹿之战。有苗之征。则此亦为小康。而不可谓之大同乎。此不过不识时势。苟为大言者之绪论也。礼记之书。大抵多出于汉儒之傅会。有不可尽信者也。观于此等处。可见矣。
问。体魂则降。知气在上。敢问何谓知气也。曰。小注临川吴氏说。不曰知气。谓神识魂乎。
又问。朱子之言曰。人赋气成形之后。理与气合。便能知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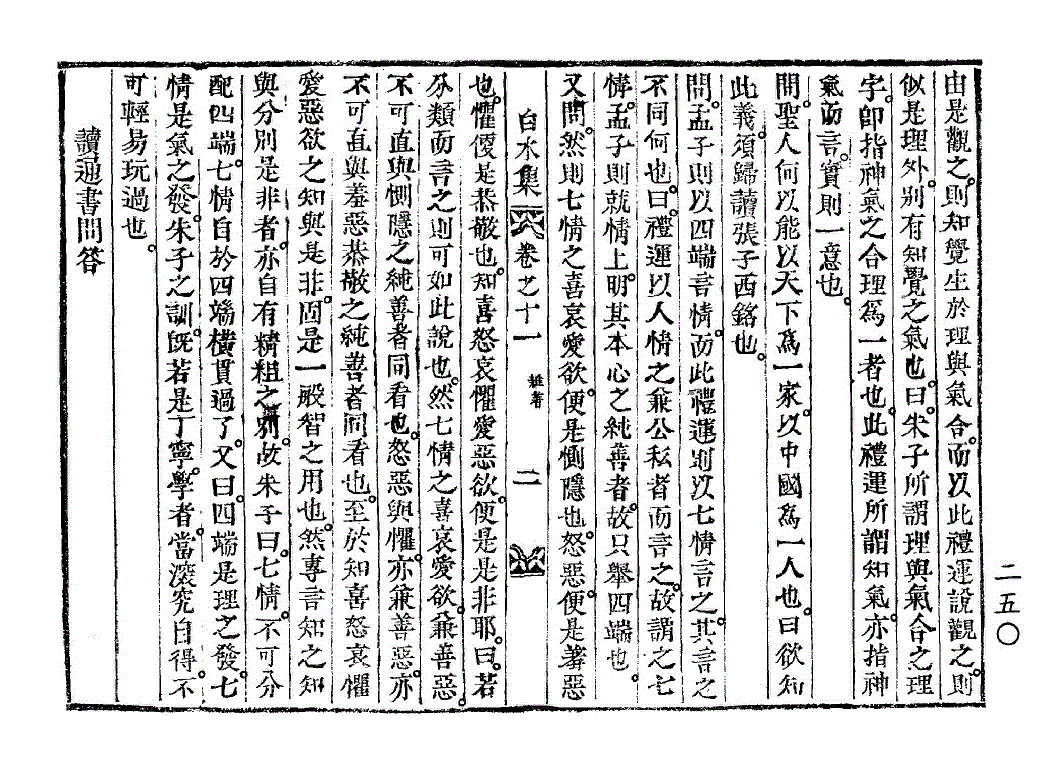 由是观之。则知觉生于理与气合。而以此礼运说观之。则似是理外。别有知觉之气也。曰。朱子所谓理与气合之理字。即指神气之合理为一者也。此礼运所谓知气。亦指神气而言。实则一意也。
由是观之。则知觉生于理与气合。而以此礼运说观之。则似是理外。别有知觉之气也。曰。朱子所谓理与气合之理字。即指神气之合理为一者也。此礼运所谓知气。亦指神气而言。实则一意也。问。圣人何以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也。曰欲知此义。须归读张子西铭也。
问。孟子则以四端言情。而此礼运则以七情言之。其言之不同何也。曰。礼运以人情之兼公私者而言之。故谓之七情。孟子则就情上。明其本心之纯善者。故只举四端也。
又问。然则七情之喜哀爱欲。便是恻隐也。怒恶。便是羞恶也。惧便是恭敬也。知喜怒哀惧爱恶欲。便是是非耶。曰。若分类而言之则可如此说也。然七情之喜哀爱欲。兼善恶。不可直与恻隐之纯善者同看也。怒恶与惧。亦兼善恶。亦不可直与羞恶恭敬之纯善者同看也。至于知喜怒哀惧爱恶欲之知与是非。固是一般智之用也。然专言知之知与分别是非者。亦自有精粗之别。故朱子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又曰。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朱子之训。既若是丁宁。学者。当深究自得。不可轻易玩过也。
读通书问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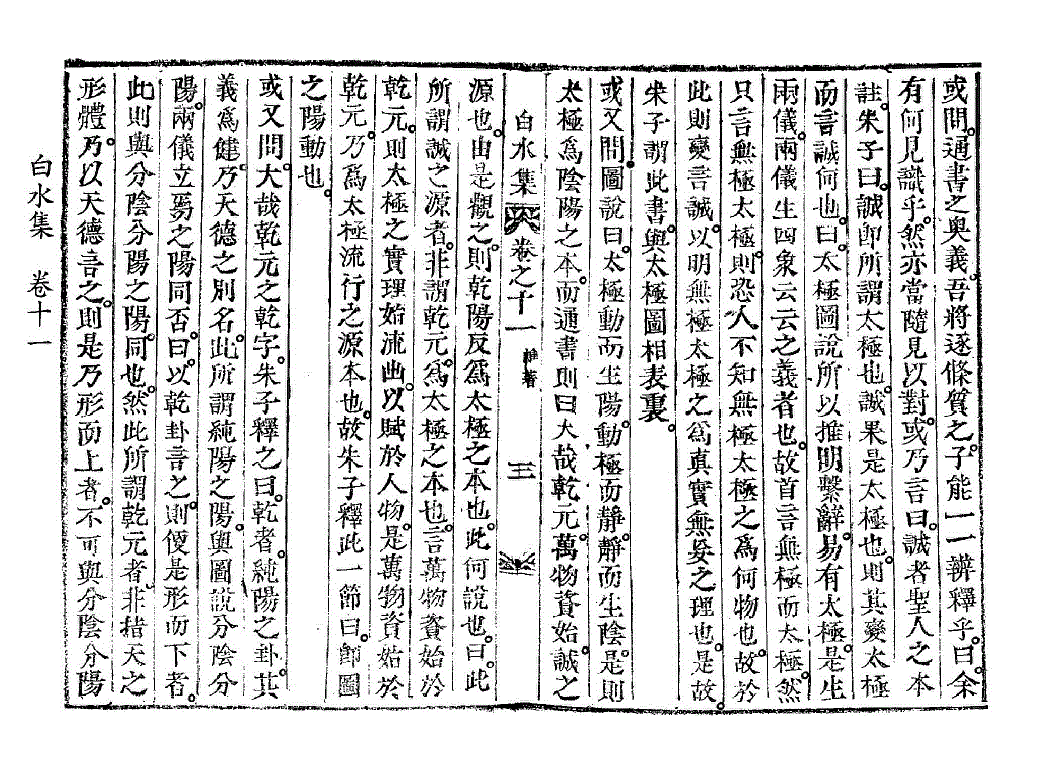 或问。通书之奥义。吾将逐条质之。子能一一辨释乎。曰。余有何见识乎。然亦当随见以对。或乃言曰。诚者圣人之本注。朱子曰。诚即所谓太极也。诚果是太极也。则其变太极而言诚何也。曰。太极图说所以推明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云云之义者也。故首言无极而太极。然只言无极太极。则恐人不知无极太极之为何物也。故于此则变言诚。以明无极太极之为真实无妄之理也。是故。朱子谓此书。与太极图相表里。
或问。通书之奥义。吾将逐条质之。子能一一辨释乎。曰。余有何见识乎。然亦当随见以对。或乃言曰。诚者圣人之本注。朱子曰。诚即所谓太极也。诚果是太极也。则其变太极而言诚何也。曰。太极图说所以推明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云云之义者也。故首言无极而太极。然只言无极太极。则恐人不知无极太极之为何物也。故于此则变言诚。以明无极太极之为真实无妄之理也。是故。朱子谓此书。与太极图相表里。或又问。图说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是则太极为阴阳之本。而通书则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由是观之。则乾阳反为太极之本也。此何说也。曰。此所谓诚之源者。非谓乾元。为太极之本也。言万物资始于乾元。则太极之实理始流出。以赋于人物。是万物资始于乾元。乃为太极流行之源本也。故朱子释此一节曰。即图之阳动也。
或又问。大哉乾元之乾字。朱子释之曰。乾者。纯阳之卦。其义为健。乃天德之别名。此所谓纯阳之阳。与图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阳同否。曰。以乾卦言之。则便是形而下者。此则与分阴分阳之阳。同也。然此所谓乾元者。非指天之形体。乃以天德言之。则是乃形而上者。不可与分阴分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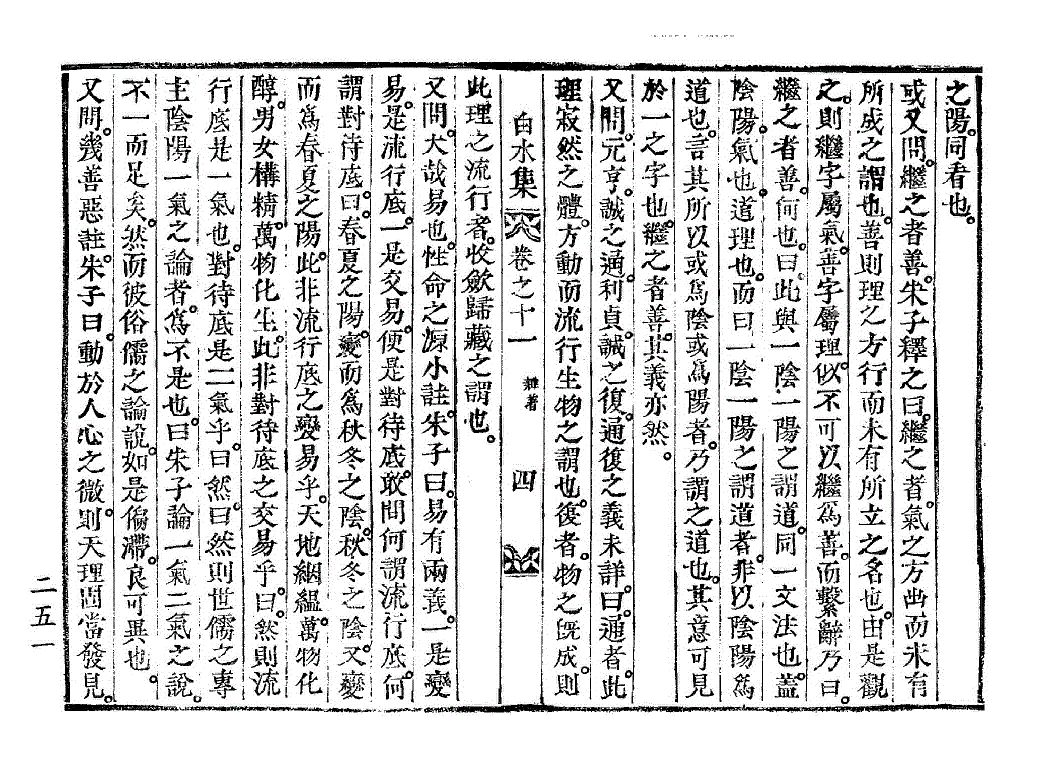 之阳。同看也。
之阳。同看也。或又问。继之者善。朱子释之曰。继之者。气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谓也。善则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由是观之。则继字属气。善字属理。似不可以继为善。而系辞乃曰。继之者善。何也。曰。此与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一文法也。盖阴阳。气也。道理也。而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者。非以阴阳为道也。言其所以或为阴或为阳者。乃谓之道也。其意可见于一之字也。继之者善。其义亦然。
又问。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通复之义未详。曰。通者。此理寂然之体。方动而流行生物之谓也。复者。物之既成。则此理之流行者。收敛归藏之谓也。
又问。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小注。朱子曰。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敢问何谓流行底。何谓对待底。曰。春夏之阳。变而为秋冬之阴。秋冬之阴。又变而为春夏之阳。此非流行底之变易乎。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非对待底之交易乎。曰。然则流行底是一气也。对待底是二气乎。曰然。曰然则世儒之专主阴阳一气之论者。为不是也。曰朱子论一气二气之说。不一而足矣。然而彼俗儒之论说。如是偏滞。良可异也。
又问。几善恶注。朱子曰。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见。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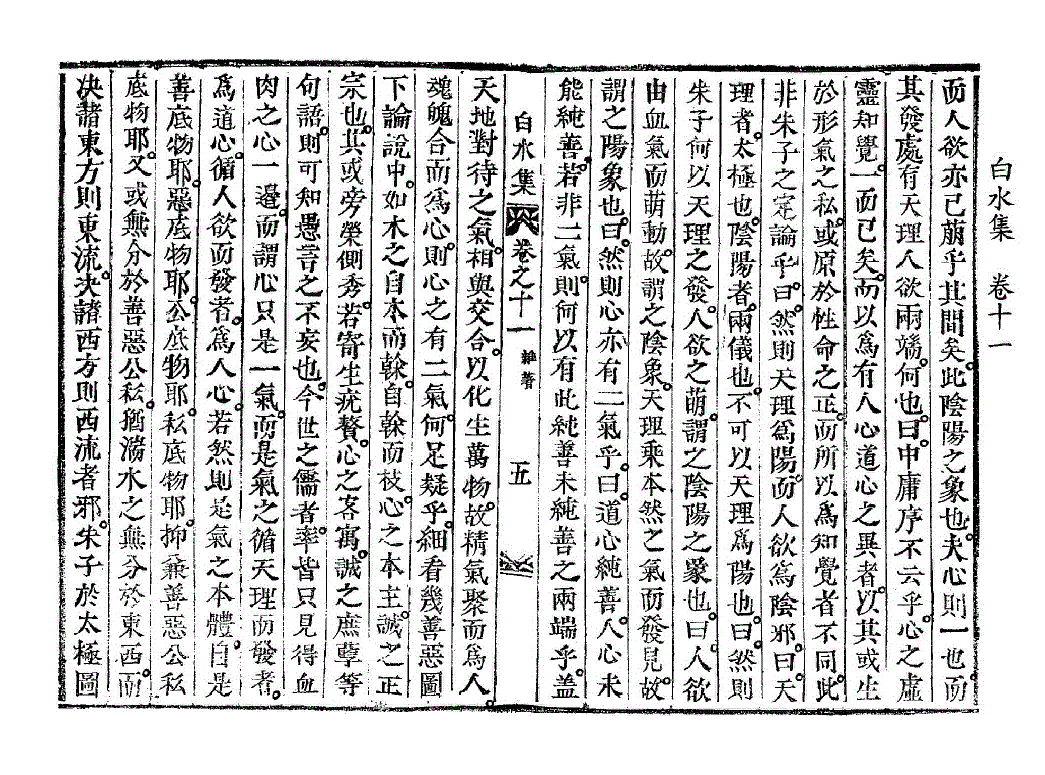 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此阴阳之象也。夫心则一也。而其发处有天理人欲两端。何也。曰。中庸序不云乎。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此非朱子之定论乎。曰。然则天理为阳。而人欲为阴邪。曰。天理者。太极也。阴阳者。两仪也。不可以天理为阳也。曰。然则朱子何以天理之发。人欲之萌。谓之阴阳之象也。曰。人欲由血气而萌动。故谓之阴象。天理乘本然之气而发见。故谓之阳象也。曰。然则心亦有二气乎。曰。道心纯善。人心未能纯善。若非二气。则何以有此纯善未纯善之两端乎。盖天地对待之气。相与交合。以化生万物。故精气聚而为人。魂魄合而为心。则心之有二气。何足疑乎。细看几善恶图下论说中。如木之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心之本主。诚之正宗也。其或旁荣侧秀。若寄生疣赘。心之客寓。诚之庶孽等句语。则可知愚言之不妄也。今世之儒者。率皆只见得血肉之心一边。而谓心只是一气。而是气之循天理而发者。为道心。循人欲而发者。为人心。若然则是气之本体。自是善底物耶。恶底物耶。公底物耶。私底物耶。抑兼善恶公私底物耶。又或无分于善恶公私。犹湍水之无分于东西。而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者邪。朱子于太极图
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此阴阳之象也。夫心则一也。而其发处有天理人欲两端。何也。曰。中庸序不云乎。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此非朱子之定论乎。曰。然则天理为阳。而人欲为阴邪。曰。天理者。太极也。阴阳者。两仪也。不可以天理为阳也。曰。然则朱子何以天理之发。人欲之萌。谓之阴阳之象也。曰。人欲由血气而萌动。故谓之阴象。天理乘本然之气而发见。故谓之阳象也。曰。然则心亦有二气乎。曰。道心纯善。人心未能纯善。若非二气。则何以有此纯善未纯善之两端乎。盖天地对待之气。相与交合。以化生万物。故精气聚而为人。魂魄合而为心。则心之有二气。何足疑乎。细看几善恶图下论说中。如木之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心之本主。诚之正宗也。其或旁荣侧秀。若寄生疣赘。心之客寓。诚之庶孽等句语。则可知愚言之不妄也。今世之儒者。率皆只见得血肉之心一边。而谓心只是一气。而是气之循天理而发者。为道心。循人欲而发者。为人心。若然则是气之本体。自是善底物耶。恶底物耶。公底物耶。私底物耶。抑兼善恶公私底物耶。又或无分于善恶公私。犹湍水之无分于东西。而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者邪。朱子于太极图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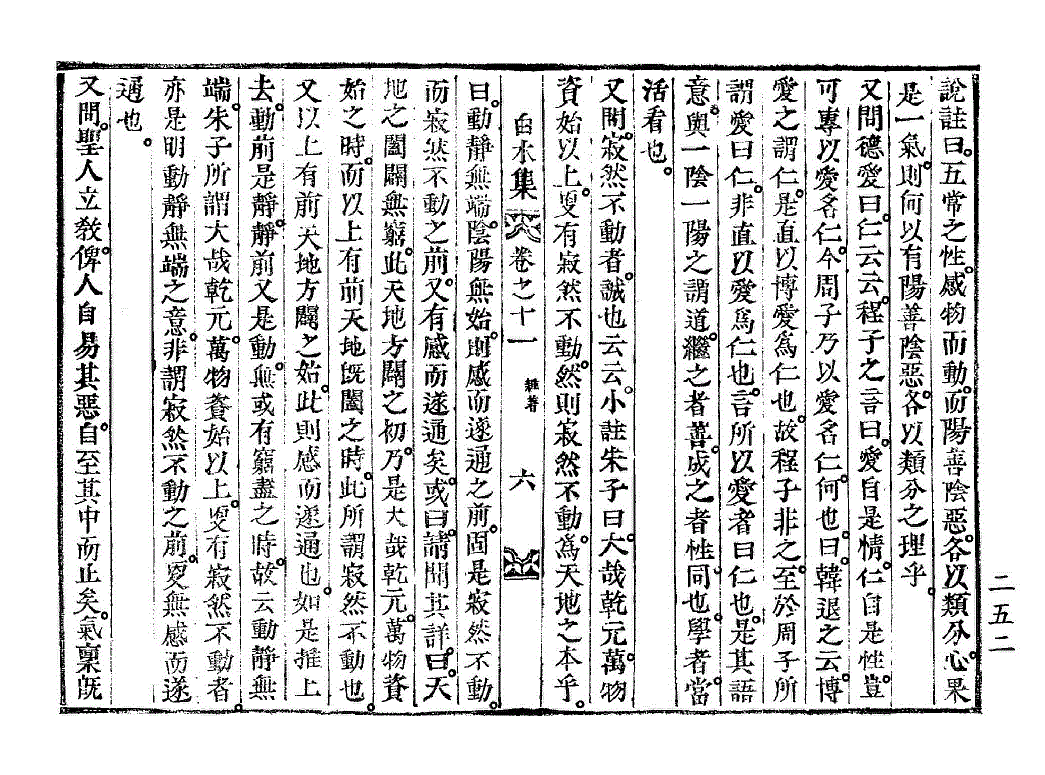 说注曰。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各以类分。心果是一气。则何以有阳善阴恶。各以类分之理乎。
说注曰。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阳善阴恶。各以类分。心果是一气。则何以有阳善阴恶。各以类分之理乎。又问德爱曰。仁云云。程子之言曰。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名仁。今周子乃以爱名仁。何也。曰。韩退之云。博爱之谓仁。是直以博爱为仁也。故程子非之。至于周子所谓爱曰仁。非直以爱为仁也。言所以爱者曰仁也。是其语意。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同也。学者。当活看也。
又问。寂然不动者。诚也云云。小注朱子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动。然则寂然不动。为天地之本乎。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感而遂通之前。固是寂然不动。而寂然不动之前。又有感而遂通矣。或曰。请闻其详。曰。天地之阖辟无穷。此天地方辟之初。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时。而以上有前天地既阖之时。此所谓寂然不动也。又以上有前天地方辟之始。此则感而遂通也。如是推上去。动前是静。静前又是动。无或有穷尽之时。故云动静无端。朱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动者。亦是明动静无端之意。非谓寂然不动之前。更无感而遂通也。
又问。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气禀既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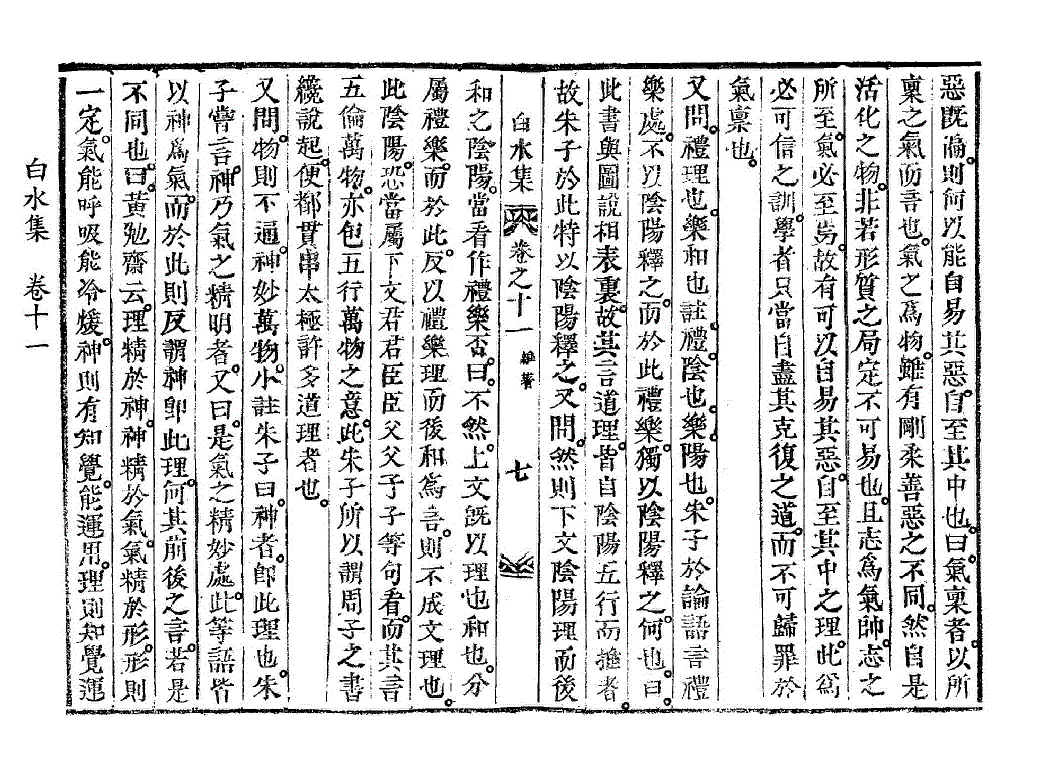 恶既偏。则何以能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也。曰。气禀者。以所禀之气而言也。气之为物。虽有刚柔善恶之不同。然自是活化之物。非若形质之局定不可易也。且志为气帅。志之所至。气必至焉。故有可以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之理。此为必可信之训。学者只当自尽其克复之道。而不可归罪于气禀也。
恶既偏。则何以能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也。曰。气禀者。以所禀之气而言也。气之为物。虽有刚柔善恶之不同。然自是活化之物。非若形质之局定不可易也。且志为气帅。志之所至。气必至焉。故有可以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之理。此为必可信之训。学者只当自尽其克复之道。而不可归罪于气禀也。又问。礼理也。乐和也注。礼。阴也。乐。阳也。朱子于论语言礼乐处。不以阴阳释之。而于此礼乐。独以阴阳释之。何也。曰。此书与图说相表里。故其言道理。皆自阴阳五行而推者。故朱子于此特以阴阳释之。又问。然则下文阴阳理而后和之阴阳。当看作礼乐否。曰。不然。上文既以理也和也。分属礼乐。而于此。反以礼乐理而后和为言。则不成文理也。此阴阳。恐当属下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句看。而其言五伦万物。亦包五行万物之意。此朱子所以谓周子之书才说起。便都贯串太极许多道理者也。
又问。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小注朱子曰。神者。即此理也。朱子尝言。神乃气之精明者。又曰。是气之精妙处。此等语皆以神为气。而于此则反谓神即此理。何其前后之言。若是不同也。曰。黄勉斋云。理精于神。神精于气。气精于形。形则一定。气能呼吸能冷煖。神则有知觉。能运用。理则知觉运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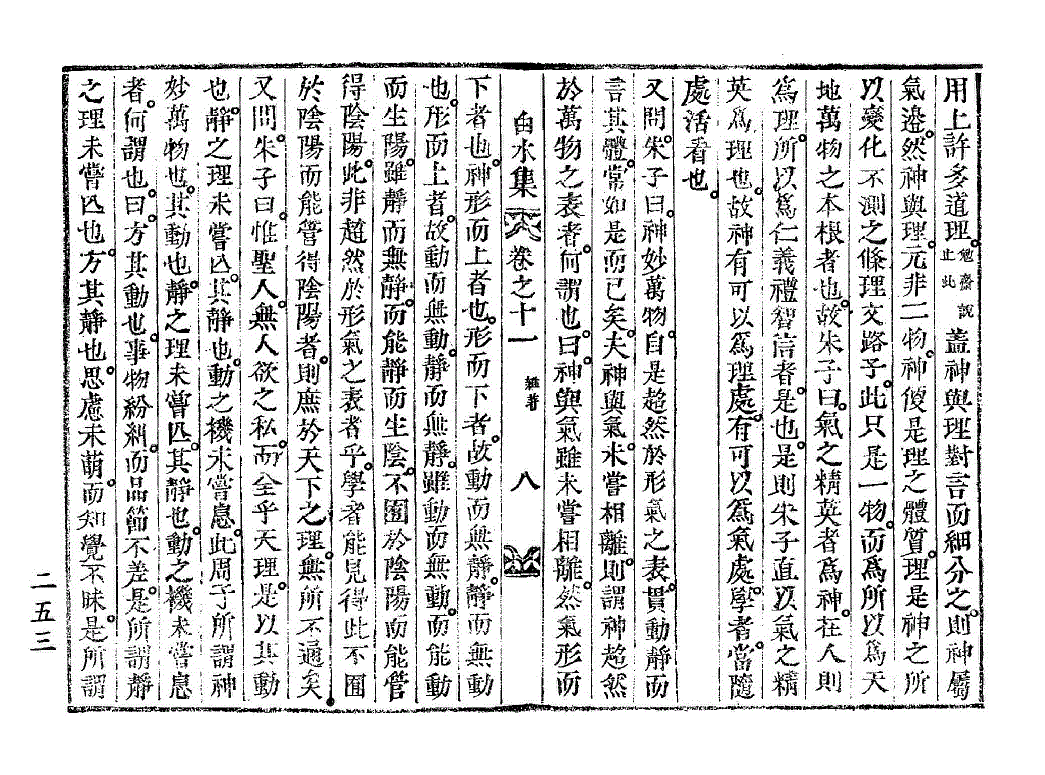 用上许多道理。(勉斋说止此)盖神与理对言而细分之。则神属气边。然神与理。元非二物。神便是理之体质。理是神之所以变化不测之条理文路子。此只是一物。而为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本根者也。故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是则朱子直以气之精英为理也。故神有可以为理处。有可以为气处。学者。当随处活看也。
用上许多道理。(勉斋说止此)盖神与理对言而细分之。则神属气边。然神与理。元非二物。神便是理之体质。理是神之所以变化不测之条理文路子。此只是一物。而为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本根者也。故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是则朱子直以气之精英为理也。故神有可以为理处。有可以为气处。学者。当随处活看也。又问。朱子曰。神妙万物。自是超然于形气之表。贯动静而言其体。常如是而已矣。夫神与气。未尝相离。则谓神超然于万物之表者。何谓也。曰。神与气虽未尝相离。然气形而下者也。神形而上者也。形而下者。故动而无静。静而无动也。形而上者。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虽动而无动。而能动而生阳。虽静而无静。而能静而生阴。不囿于阴阳而能管得阴阳。此非超然于形气之表者乎。学者能见得此不囿于阴阳而能管得阴阳者。则庶于天下之理。无所不通矣。
又问。朱子曰。惟圣人。无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动也。静之理未尝亡。其静也。动之机未尝息。此周子所谓神妙万物也。其动也。静之理未尝亡。其静也。动之机未尝息者。何谓也。曰。方其动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所谓静之理未尝亡也。方其静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所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4H 页
 动之机未尝息者也。
动之机未尝息者也。又问。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五行之气。莫非阴阳之气。则谓阴阳为五行。可至于太极。阴阳则不然。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其可以形而下之阴阳。直谓之形而上之太极乎。曰。太极阴阳。固有形上下之分。然究阴阳之所自生。则太极也。故自五行而言阴阳。自阴阳而言太极。是乃推本言之也。非以形而下之阴阳。直谓之形而上之太极也。
又问。混兮辟兮。其无穷兮。此二句。以大注及小注观之。则为开合循环无穷之意也。以章下小注观之。则为但言生生不穷之意也。学者将何所适从也。曰。当从上注说。
又问。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云云。小注朱子曰。周子只说一者无欲也。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只说个敬字。由是观之。则周子似无敬字工夫。如是而能得无欲乎。曰。孔子答颜渊之问仁。只言克己复礼为仁。未尝言敬。若以是而疑颜子不能尽克复之道则可乎。盖颜子资质甚高。其明甚刚。不待敬而足以能克己复礼。故夫子直言克己复礼而不言敬也。周先生资禀之高如颜子。故亦不待敬而能无欲也。观其所谓果而确。无难焉之语。可知矣。所以其言之高如此也。然他人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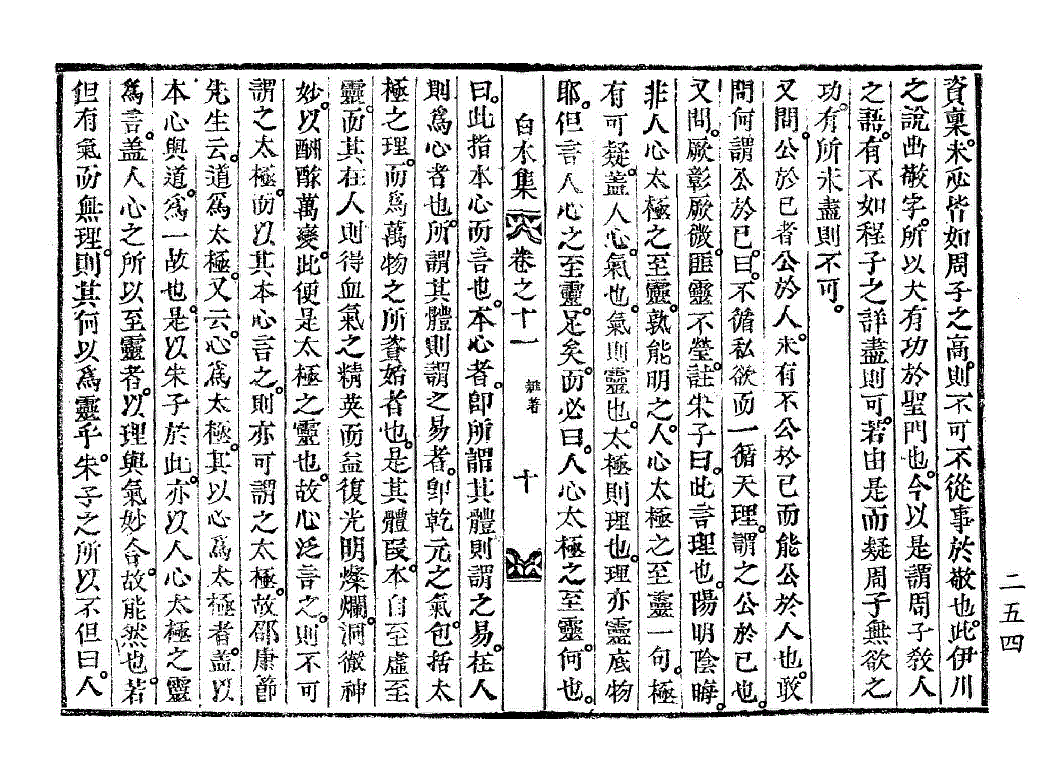 资禀。未必皆如周子之高。则不可不从事于敬也。此伊川之说出敬字。所以大有功于圣门也。今以是谓周子教人之语。有不如程子之详尽则可。若由是而疑周子无欲之功。有所未尽则不可。
资禀。未必皆如周子之高。则不可不从事于敬也。此伊川之说出敬字。所以大有功于圣门也。今以是谓周子教人之语。有不如程子之详尽则可。若由是而疑周子无欲之功。有所未尽则不可。又问。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敢问何谓公于己。曰。不循私欲而一循天理。谓之公于己也。
又问。厥彰厥微。匪灵不莹。注朱子曰。此言理也。阳明阴晦。非人心太极之至灵。孰能明之。人心太极之至灵一句。极有可疑。盖人心。气也。气则灵也。太极则理也。理亦灵底物耶。但言人心之至灵。足矣。而必曰。人心太极之至灵。何也。曰。此指本心而言也。本心者。即所谓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为心者也。所谓其体则谓之易者。即乾元之气。包括太极之理。而为万物之所资始者也。是其体段。本自至虚至灵。而其在人则得血气之精英而益复光明灿烂。洞彻神妙。以酬酢万变。此便是太极之灵也。故心泛言之。则不可谓之太极。而以其本心言之。则亦可谓之太极。故邵康节先生云。道为太极。又云。心为太极。其以心为太极者。盖以本心与道。为一故也。是以朱子于此。亦以人心太极之灵为言。盖人心之所以至灵者。以理与气妙合。故能然也。若但有气而无理。则其何以为灵乎。朱子之所以不但曰。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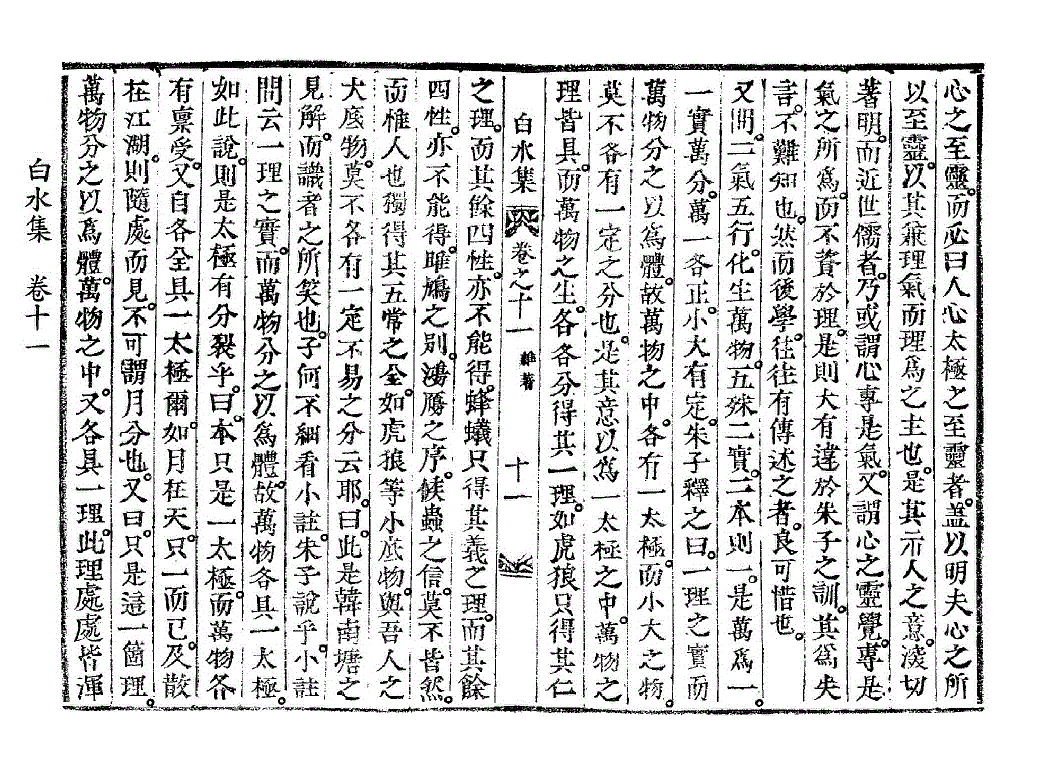 心之至灵。而必曰人心太极之至灵者。盖以明夫心之所以至灵。以其兼理气而理为之主也。是其示人之意。深切著明。而近世儒者。乃或谓心专是气。又谓心之灵觉。专是气之所为。而不资于理。是则大有违于朱子之训。其为失言。不难知也。然而后学。往往有传述之者。良可惜也。
心之至灵。而必曰人心太极之至灵者。盖以明夫心之所以至灵。以其兼理气而理为之主也。是其示人之意。深切著明。而近世儒者。乃或谓心专是气。又谓心之灵觉。专是气之所为。而不资于理。是则大有违于朱子之训。其为失言。不难知也。然而后学。往往有传述之者。良可惜也。又问。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朱子释之曰。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是其意以为一太极之中。万物之理皆具。而万物之生。各各分得其一理。如虎狼只得其仁之理。而其馀四性。亦不能得。蜂蚁只得其义之理。而其馀四性。亦不能得。雎鸠之别。鸿雁之序。候虫之信。莫不皆然。而惟人也独得其五常之全。如虎狼等小底物。与吾人之大底物。莫不各有一定不易之分云耶。曰。此是韩南塘之见解。而识者之所笑也。子何不细看小注。朱子说乎。小注问云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是太极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又曰。只是这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此理处处皆浑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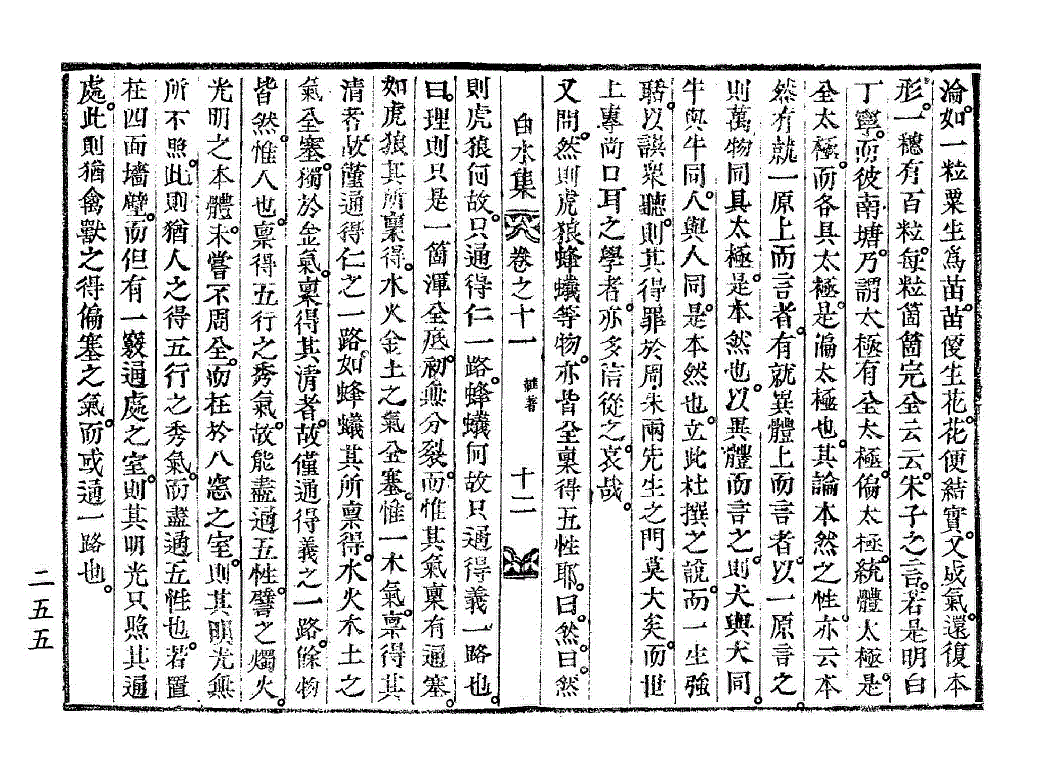 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气。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云云。朱子之言。若是明白丁宁。而彼南塘。乃谓太极有全太极。偏太极。统体太极。是全太极。而各具太极。是偏太极也。其论本然之性。亦云本然有就一原上而言者。有就异体上而言者。以一原言之。则万物同具太极。是本然也。以异体而言之。则犬与犬同。牛与牛同。人与人同。是本然也。立此杜撰之说。而一生强聒。以误众听。则其得罪于周,朱两先生之门莫大矣。而世上专尚口耳之学者。亦多信从之。哀哉。
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气。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云云。朱子之言。若是明白丁宁。而彼南塘。乃谓太极有全太极。偏太极。统体太极。是全太极。而各具太极。是偏太极也。其论本然之性。亦云本然有就一原上而言者。有就异体上而言者。以一原言之。则万物同具太极。是本然也。以异体而言之。则犬与犬同。牛与牛同。人与人同。是本然也。立此杜撰之说。而一生强聒。以误众听。则其得罪于周,朱两先生之门莫大矣。而世上专尚口耳之学者。亦多信从之。哀哉。又问。然则虎狼蜂蚁等物。亦皆全禀得五性耶。曰。然。曰。然则虎狼何故。只通得仁一路。蜂蚁何故只通得义一路也。曰。理则只是一个浑全底。初无分裂。而惟其气禀有通塞。如虎狼其所禀得。水火金土之气全塞。惟一木气。禀得其清者。故仅通得仁之一路。如蜂蚁其所禀得。水火木土之气全塞。独于金气。禀得其清者。故仅通得义之一路。馀物皆然。惟人也。禀得五行之秀气。故能尽通五性。譬之烛火。光明之本体。未尝不周全。而在于八窗之室。则其明光无所不照。此则犹人之得五行之秀气。而尽通五性也。若置在四面墙壁。而但有一窍通处之室。则其明光只照其通处。此则犹禽兽之得偏塞之气。而或通一路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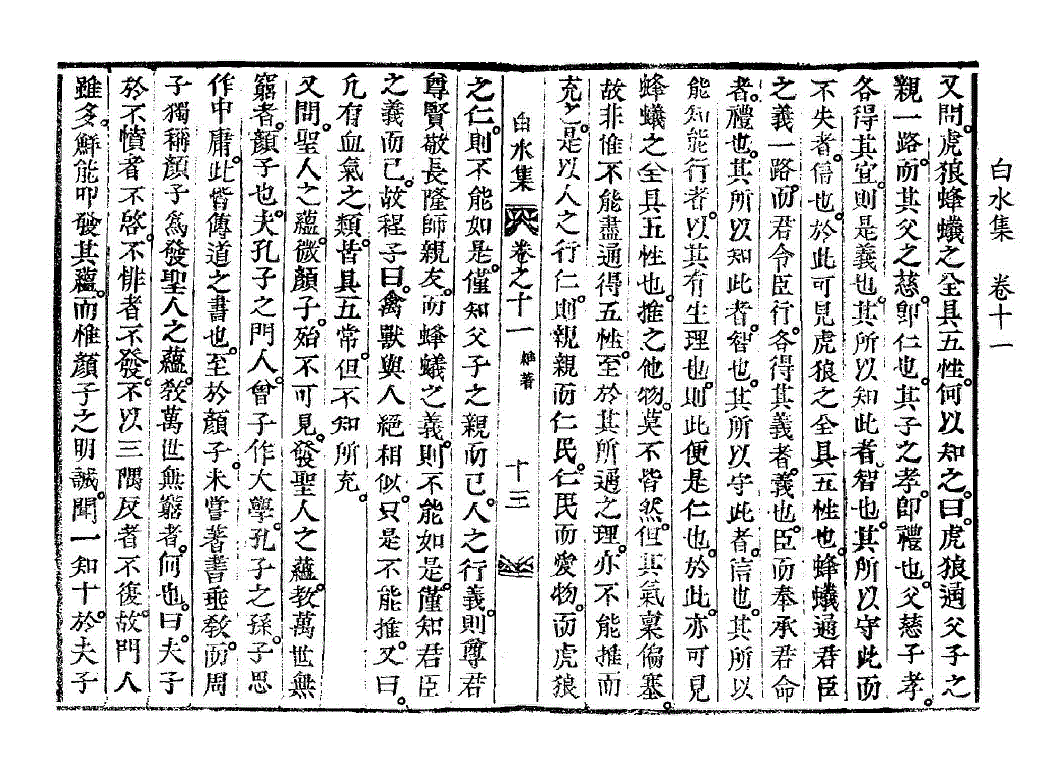 又问。虎狼蜂蚁之全具五性。何以知之。曰。虎狼通父子之亲一路。而其父之慈。即仁也。其子之孝。即礼也。父慈子孝。各得其宜。则是义也。其所以知此者。智也。其所以守此而不失者。信也。于此可见虎狼之全具五性也。蜂蚁通君臣之义一路。而君令臣行。各得其义者。义也。臣而奉承君命者。礼也。其所以知此者。智也。其所以守此者。信也。其所以能知能行者。以其有生理也。则此便是仁也。于此。亦可见蜂蚁之全具五性也。推之他物。莫不皆然。但其气禀偏塞。故非惟不能尽通得五性。至于其所通之理。亦不能推而充之。是以人之行仁。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虎狼之仁。则不能如是。仅知父子之亲而已。人之行义。则尊君尊贤敬长隆师亲友。而蜂蚁之义。则不能如是。仅知君臣之义而已。故程子曰。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又曰。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所充。
又问。虎狼蜂蚁之全具五性。何以知之。曰。虎狼通父子之亲一路。而其父之慈。即仁也。其子之孝。即礼也。父慈子孝。各得其宜。则是义也。其所以知此者。智也。其所以守此而不失者。信也。于此可见虎狼之全具五性也。蜂蚁通君臣之义一路。而君令臣行。各得其义者。义也。臣而奉承君命者。礼也。其所以知此者。智也。其所以守此者。信也。其所以能知能行者。以其有生理也。则此便是仁也。于此。亦可见蜂蚁之全具五性也。推之他物。莫不皆然。但其气禀偏塞。故非惟不能尽通得五性。至于其所通之理。亦不能推而充之。是以人之行仁。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虎狼之仁。则不能如是。仅知父子之亲而已。人之行义。则尊君尊贤敬长隆师亲友。而蜂蚁之义。则不能如是。仅知君臣之义而已。故程子曰。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又曰。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所充。又问。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夫孔子之门人。曾子作大学。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此皆传道之书也。至于颜子。未尝著书垂教。而周子独称颜子为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何也。曰。夫子于不愤者不启。不悱者不发。不以三隅反者不复。故门人虽多。鲜能叩发其蕴。而惟颜子之明诚。闻一知十。于夫子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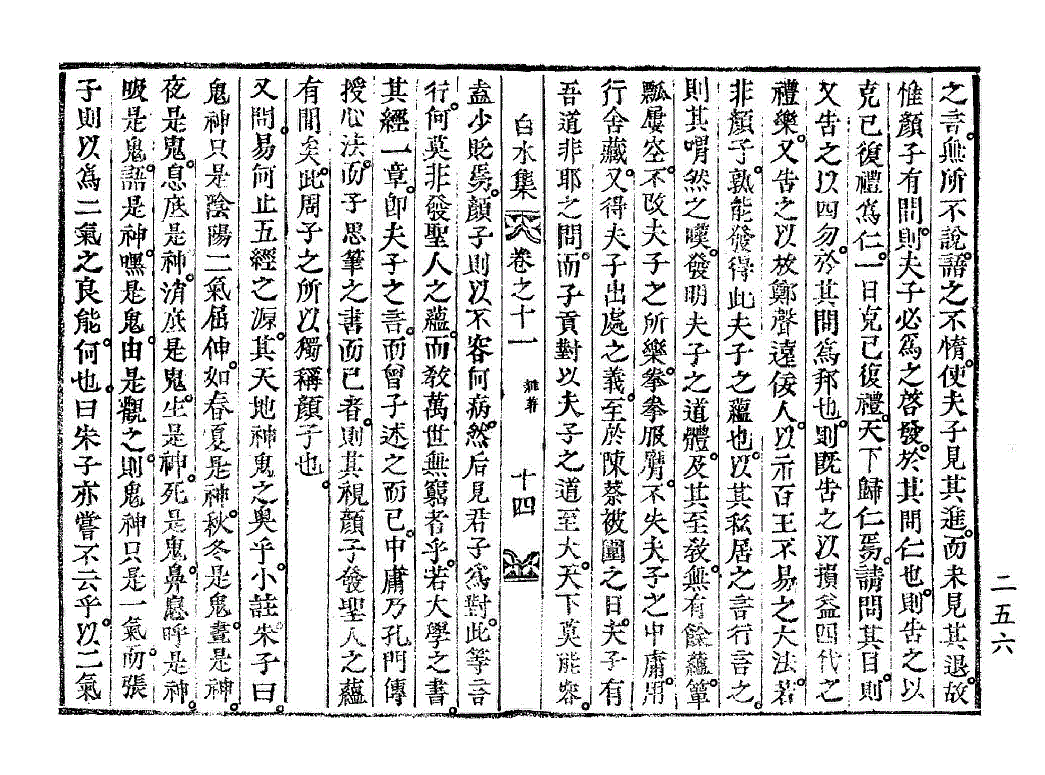 之言。无所不说。语之不惰。使夫子见其进。而未见其退。故惟颜子有问。则夫子必为之启发。于其问仁也。则告之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请问其目。则又告之以四勿。于其问为邦也。则既告之以损益四代之礼乐。又告之以放郑声远佞人。以示百王不易之大法。若非颜子。孰能发得此夫子之蕴也。以其私居之言行言之。则其喟然之叹。发明夫子之道体。及其至教。无有馀蕴。箪瓢屡空。不改夫子之所乐。拳拳服膺。不失夫子之中庸。用行舍藏。又得夫子出处之义。至于陈蔡被围之日。夫子有吾道非耶之问。而子贡对以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颜子则以不容何病。然后见君子为对。此等言行。何莫非发圣人之蕴。而教万世无穷者乎。若大学之书。其经一章。即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已。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而子思笔之书而已者。则其视颜子发圣人之蕴有间矣。此周子之所以独称颜子也。
之言。无所不说。语之不惰。使夫子见其进。而未见其退。故惟颜子有问。则夫子必为之启发。于其问仁也。则告之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请问其目。则又告之以四勿。于其问为邦也。则既告之以损益四代之礼乐。又告之以放郑声远佞人。以示百王不易之大法。若非颜子。孰能发得此夫子之蕴也。以其私居之言行言之。则其喟然之叹。发明夫子之道体。及其至教。无有馀蕴。箪瓢屡空。不改夫子之所乐。拳拳服膺。不失夫子之中庸。用行舍藏。又得夫子出处之义。至于陈蔡被围之日。夫子有吾道非耶之问。而子贡对以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颜子则以不容何病。然后见君子为对。此等言行。何莫非发圣人之蕴。而教万世无穷者乎。若大学之书。其经一章。即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已。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而子思笔之书而已者。则其视颜子发圣人之蕴有间矣。此周子之所以独称颜子也。又问。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神鬼之奥乎。小注。朱子曰。鬼神只是阴阳二气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昼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语是神。嘿是鬼。由是观之。则鬼神只是一气。而张子则以为二气之良能。何也。曰朱子亦尝不云乎。以二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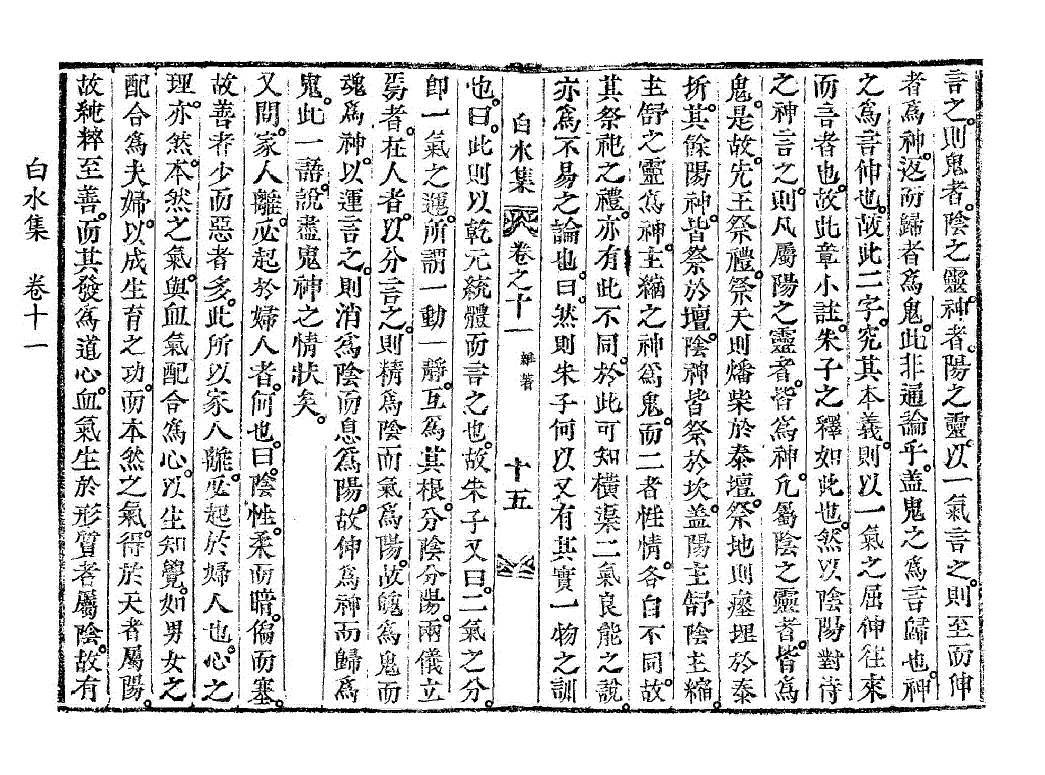 言之。则鬼者。阴之灵。神者。阳之灵。以一气言之。则至而伸者为神。返而归者为鬼。此非通论乎。盖鬼之为言归也。神之为言伸也。故此二字。究其本义。则以一气之屈伸往来而言者也。故此章小注。朱子之释如此也。然以阴阳对待之神言之。则凡属阳之灵者。皆为神。凡属阴之灵者。皆为鬼。是故。先王祭礼。祭天则燔柴于泰坛。祭地则瘗埋于泰圻。其馀阳神。皆祭于坛。阴神皆祭于坎。盖阳主舒阴主缩。主舒之灵为神。主缩之神为鬼。而二者性情。各自不同。故其祭祀之礼。亦有此不同。于此可知横渠二气良能之说。亦为不易之论也。曰。然则朱子何以又有其实一物之训也。曰。此则以乾元统体而言之也。故朱子又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在人者。以分言之。则精为阴而气为阳。故魄为鬼而魂为神。以运言之。则消为阴而息为阳。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一语。说尽鬼神之情状矣。
言之。则鬼者。阴之灵。神者。阳之灵。以一气言之。则至而伸者为神。返而归者为鬼。此非通论乎。盖鬼之为言归也。神之为言伸也。故此二字。究其本义。则以一气之屈伸往来而言者也。故此章小注。朱子之释如此也。然以阴阳对待之神言之。则凡属阳之灵者。皆为神。凡属阴之灵者。皆为鬼。是故。先王祭礼。祭天则燔柴于泰坛。祭地则瘗埋于泰圻。其馀阳神。皆祭于坛。阴神皆祭于坎。盖阳主舒阴主缩。主舒之灵为神。主缩之神为鬼。而二者性情。各自不同。故其祭祀之礼。亦有此不同。于此可知横渠二气良能之说。亦为不易之论也。曰。然则朱子何以又有其实一物之训也。曰。此则以乾元统体而言之也。故朱子又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在人者。以分言之。则精为阴而气为阳。故魄为鬼而魂为神。以运言之。则消为阴而息为阳。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一语。说尽鬼神之情状矣。又问。家人离。必起于妇人者。何也。曰。阴性。柔而暗。偏而塞。故善者少而恶者多。此所以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也。心之理。亦然。本然之气。与血气配合为心。以生知觉。如男女之配合为夫妇。以成生育之功。而本然之气。得于天者属阳。故纯粹至善。而其发为道心。血气生于形质者属阴。故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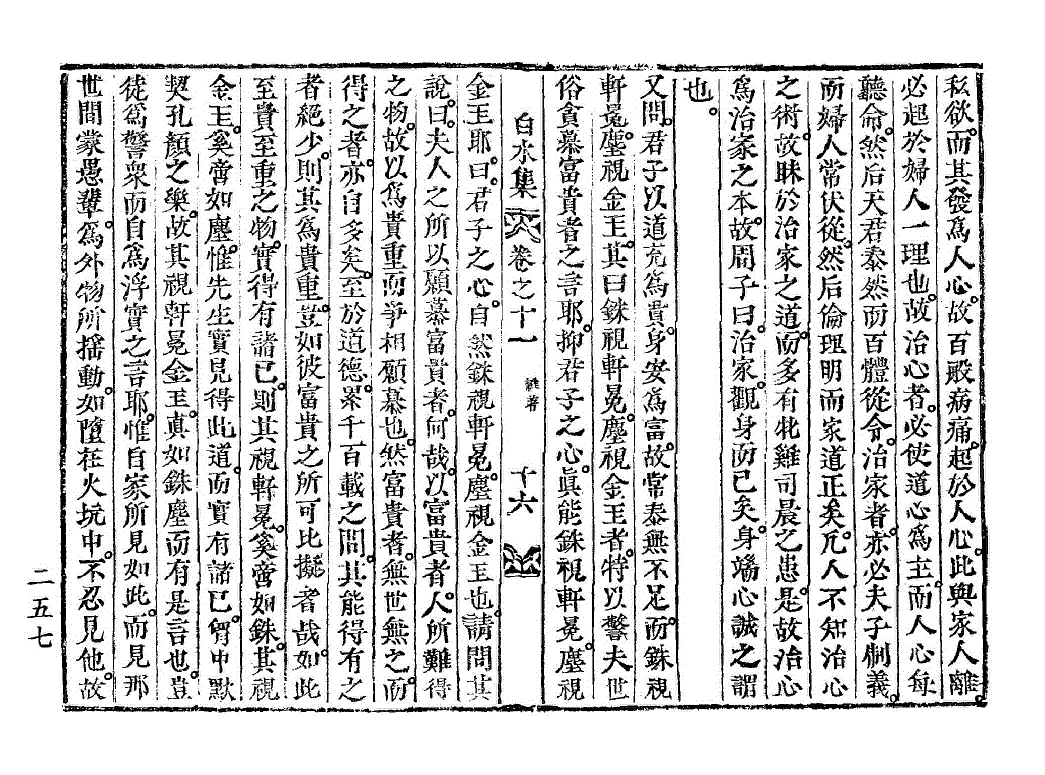 私欲。而其发为人心。故百般病痛。起于人心。此与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一理也。故治心者。必使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然后天君泰然而百体从令。治家者。亦必夫子制义。而妇人常伏从。然后伦理明而家道正矣。凡人不知治心之术。故昧于治家之道。而多有牝鸡司晨之患。是故治心为治家之本。故周子曰。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
私欲。而其发为人心。故百般病痛。起于人心。此与家人离。必起于妇人一理也。故治心者。必使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然后天君泰然而百体从令。治家者。亦必夫子制义。而妇人常伏从。然后伦理明而家道正矣。凡人不知治心之术。故昧于治家之道。而多有牝鸡司晨之患。是故治心为治家之本。故周子曰。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又问。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曰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者。特以警夫世俗贪慕富贵者之言耶。抑君子之心。真能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耶。曰。君子之心。自然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也。请问其说。曰。夫人之所以愿慕富贵者。何哉。以富贵者。人所难得之物。故以为贵重而争相愿慕也。然富贵者。无世无之。而得之者。亦自多矣。至于道德。累千百载之间。其能得有之者绝少。则其为贵重。岂如彼富贵之所可比拟者哉。如此至贵至重之物。实得有诸己。则其视轩冕。奚啻如铢。其视金玉。奚啻如尘。惟先生实见得此道。而实有诸己。胸中默契孔颜之乐。故其视轩冕金玉。真如铢尘而有是言也。岂徒为警众而自为浮实之言耶。惟自家所见如此。而见那世间蒙愚辈。为外物所摇动。如堕在火坑中。不忍见他。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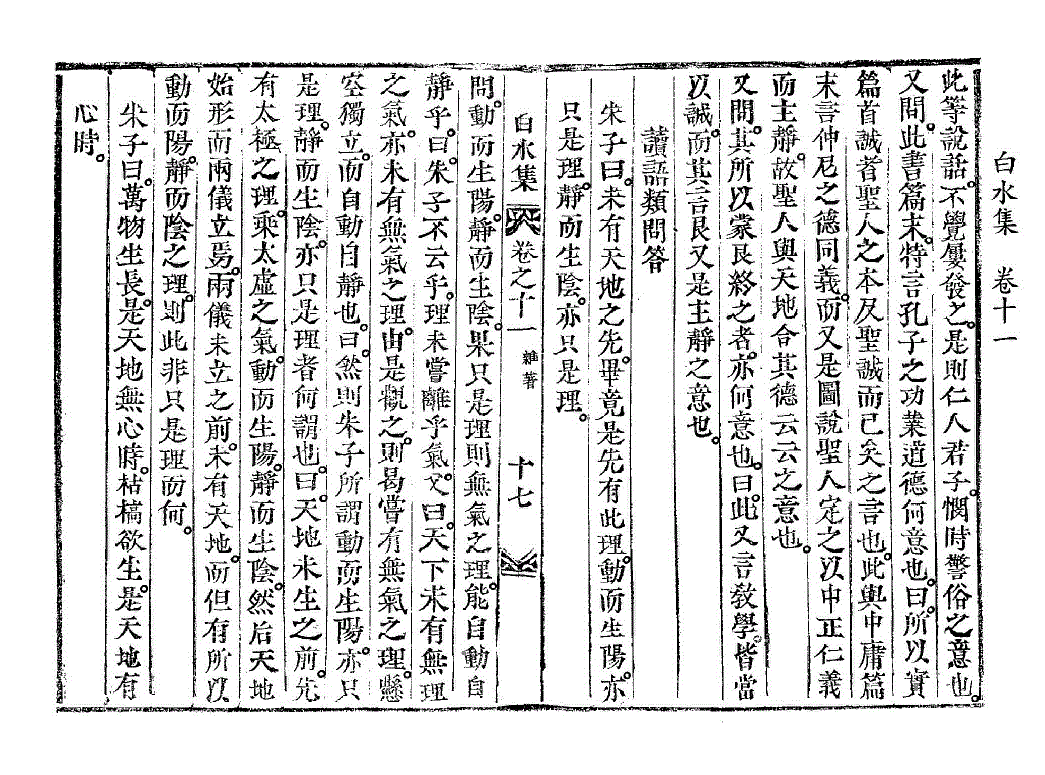 此等说话。不觉屡发之。是则仁人君子。悯时警俗之意也。
此等说话。不觉屡发之。是则仁人君子。悯时警俗之意也。又问。此书篇末。特言孔子之功业道德何意也。曰。所以实篇首诚者圣人之本及圣诚而已矣之言也。此与中庸篇末言仲尼之德同义。而又是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云云之意也。
又问。其所以蒙艮终之者。亦何意也。曰。此又言教学。皆当以诚。而其言艮又是主静之意也。
读语类问答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
问。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果只是理则无气之理。能自动自静乎。曰。朱子不云乎。理未尝离乎气。又曰。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由是观之。则曷尝有无气之理。悬空独立。而自动自静也。曰。然则朱子所谓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者何谓也。曰。天地未生之前。先有太极之理。乘太虚之气。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天地始形而两仪立焉。两仪未立之前。未有天地。而但有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理。则此非只是理而何。
朱子曰。万物生长。是天地无心时。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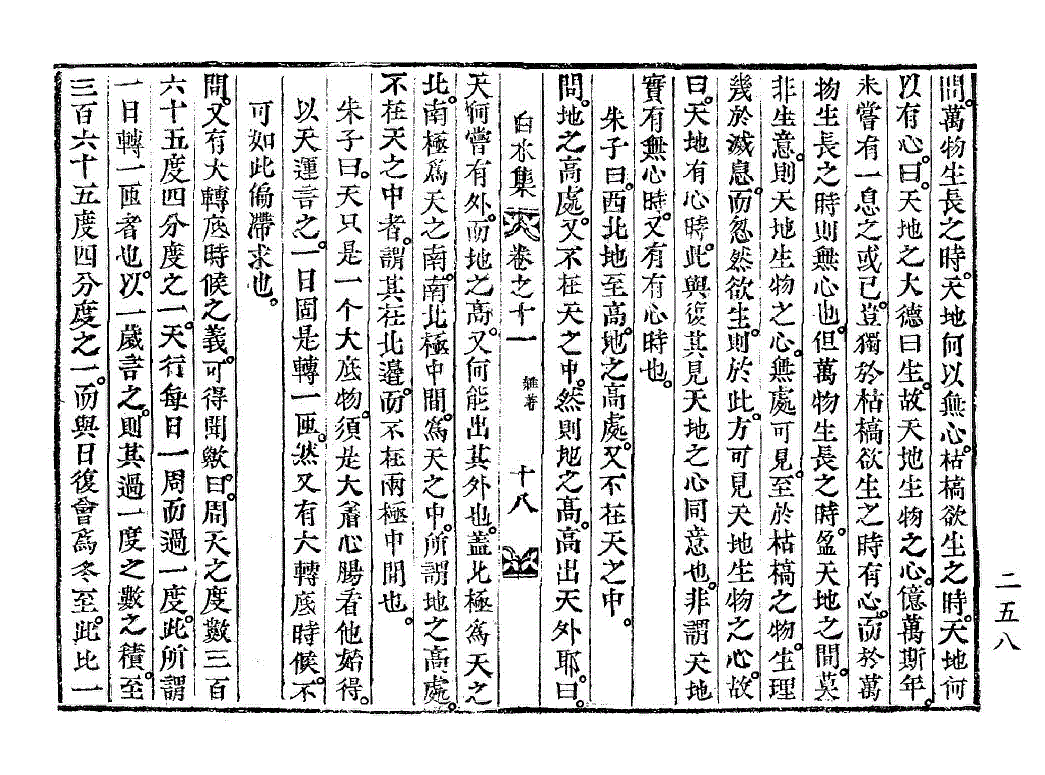 问。万物生长之时。天地何以无心。枯槁欲生之时。天地何以有心。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地生物之心。亿万斯年。未尝有一息之或已。岂独于枯槁欲生之时有心。而于万物生长之时则无心也。但万物生长之时。盈天地之间。莫非生意。则天地生物之心。无处可见。至于枯槁之物。生理几于灭息。而忽然欲生。则于此。方可见天地生物之心。故曰。天地有心时。此与复其见天地之心同意也。非谓天地实有无心时。又有有心时也。
问。万物生长之时。天地何以无心。枯槁欲生之时。天地何以有心。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地生物之心。亿万斯年。未尝有一息之或已。岂独于枯槁欲生之时有心。而于万物生长之时则无心也。但万物生长之时。盈天地之间。莫非生意。则天地生物之心。无处可见。至于枯槁之物。生理几于灭息。而忽然欲生。则于此。方可见天地生物之心。故曰。天地有心时。此与复其见天地之心同意也。非谓天地实有无心时。又有有心时也。朱子曰。西北地至高。地之高处。又不在天之中。
问。地之高处。又不在天之中。然则地之高。高出天外耶。曰。天何尝有外。而地之高。又何能出其外也。盖北极为天之北。南极为天之南。南北极中间。为天之中。所谓地之高处。不在天之中者。谓其在北边。而不在两极中间也。
朱子曰。天只是一个大底物。须是大着心肠看他。始得。以天运言之。一日固是转一匝。然又有大转底时候。不可如此偏滞求也。
问。又有大转底时候之义。可得闻欤。曰。周天之度数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每日一周而过一度。此所谓一日转一匝者也。以一岁言之。则其过一度之数之积。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与日复会为冬至。此比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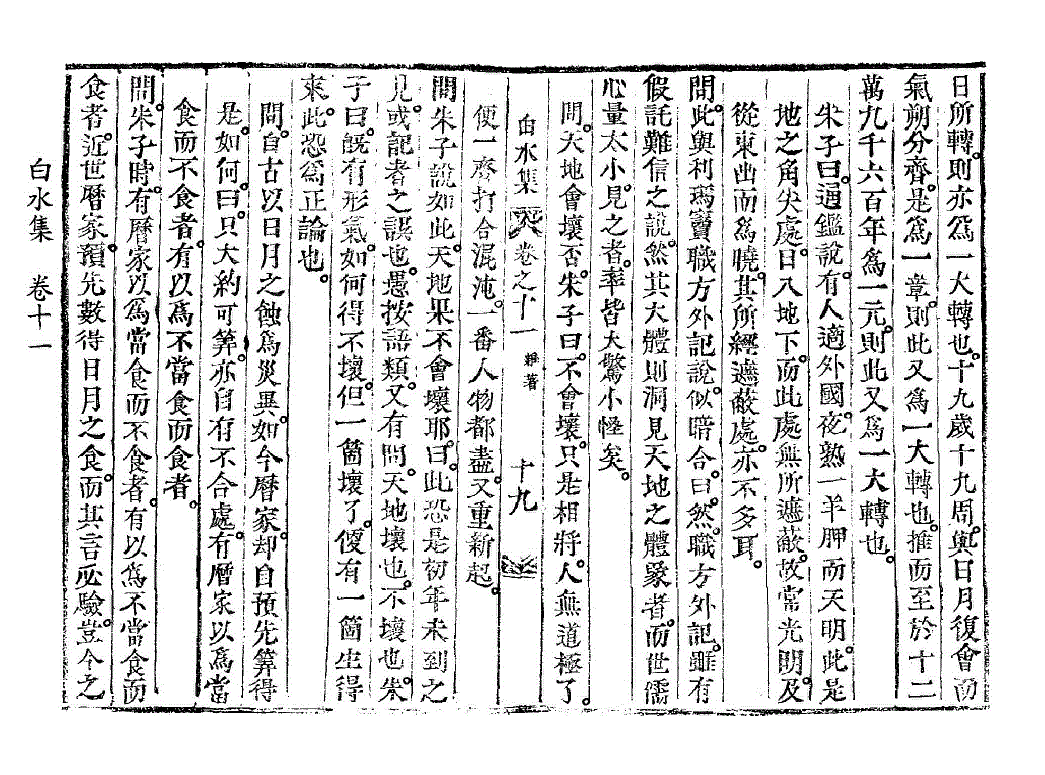 日所转。则亦为一大转也。十九岁十九周。与日月复会而气朔分齐。是为一章。则此又为一大转也。推而至于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此又为一大转也。
日所转。则亦为一大转也。十九岁十九周。与日月复会而气朔分齐。是为一章。则此又为一大转也。推而至于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此又为一大转也。朱子曰。通鉴说。有人适外国。夜熟一羊胛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处。日入地下。而此处无所遮蔽。故常光明。及从东出而为晓。其所经遮蔽处。亦不多耳。
问。此与利玛窦职方外记说。似暗合。曰。然。职方外记。虽有假托难信之说。然其大体则洞见天地之体象者。而世儒心量太小。见之者。率皆大惊小怪矣。
问。天地会坏否。朱子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问朱子说如此。天地果不会坏耶。曰。此恐是初年未到之见。或记者之误也。愚按语类。又有问。天地坏也。不坏也。朱子曰。既有形气。如何得不坏。但一个坏了。便有一个生得来。此恐为正论也。
问。自古以日月之蚀为灾异。如今历家。却自预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约可算。亦自有不合处。有历家以为当食而不食者。有以为不当食而食者。
问。朱子时。有历家以为当食而不食者。有以为不当食而食者。近世历家。预先数得日月之食。而其言必验。岂今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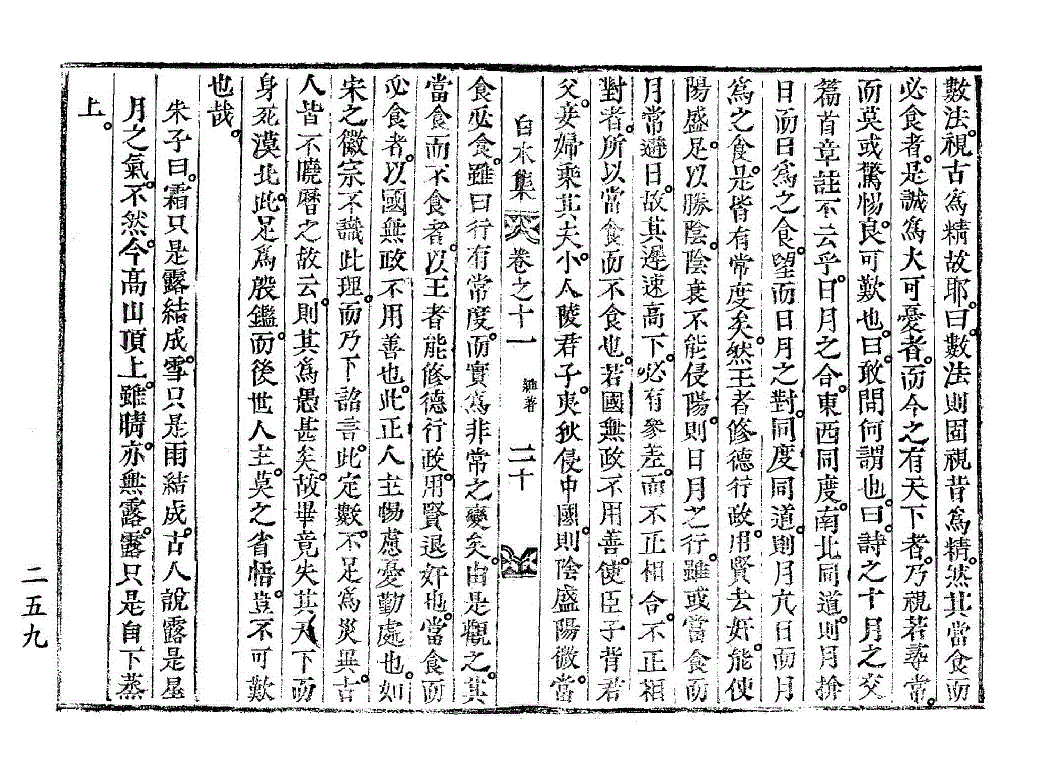 数法。视古为精故耶。曰。数法则固视昔为精。然其当食而必食者。是诚为大可忧者。而今之有天下者。乃视若寻常。而莫或惊惕。良可叹也。曰敢问何谓也。曰。诗之十月之交篇首章注不云乎。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由是观之。其当食而不食者。以王者能修德行政。用贤退奸也。当食而必食者。以国无政不用善也。此正人主惕虑忧勤处也。如宋之徽宗不识此理。而乃下诏言。此定数。不足为灾异。古人皆不晓历之故云。则其为愚甚矣。故毕竟失其天下而身死漠北。此足为殷鉴。而后世人主。莫之省悟。岂不可叹也哉。
数法。视古为精故耶。曰。数法则固视昔为精。然其当食而必食者。是诚为大可忧者。而今之有天下者。乃视若寻常。而莫或惊惕。良可叹也。曰敢问何谓也。曰。诗之十月之交篇首章注不云乎。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掩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阴衰不能侵阳。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迟速高下。必有参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对者。所以当食而不食也。若国无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妇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国。则阴盛阳微。当食必食。虽曰行有常度。而实为非常之变矣。由是观之。其当食而不食者。以王者能修德行政。用贤退奸也。当食而必食者。以国无政不用善也。此正人主惕虑忧勤处也。如宋之徽宗不识此理。而乃下诏言。此定数。不足为灾异。古人皆不晓历之故云。则其为愚甚矣。故毕竟失其天下而身死漠北。此足为殷鉴。而后世人主。莫之省悟。岂不可叹也哉。朱子曰。霜只是露结成。雪只是雨结成。古人说露是星月之气。不然。今高山顶上。虽晴。亦无露。露只是自下蒸上。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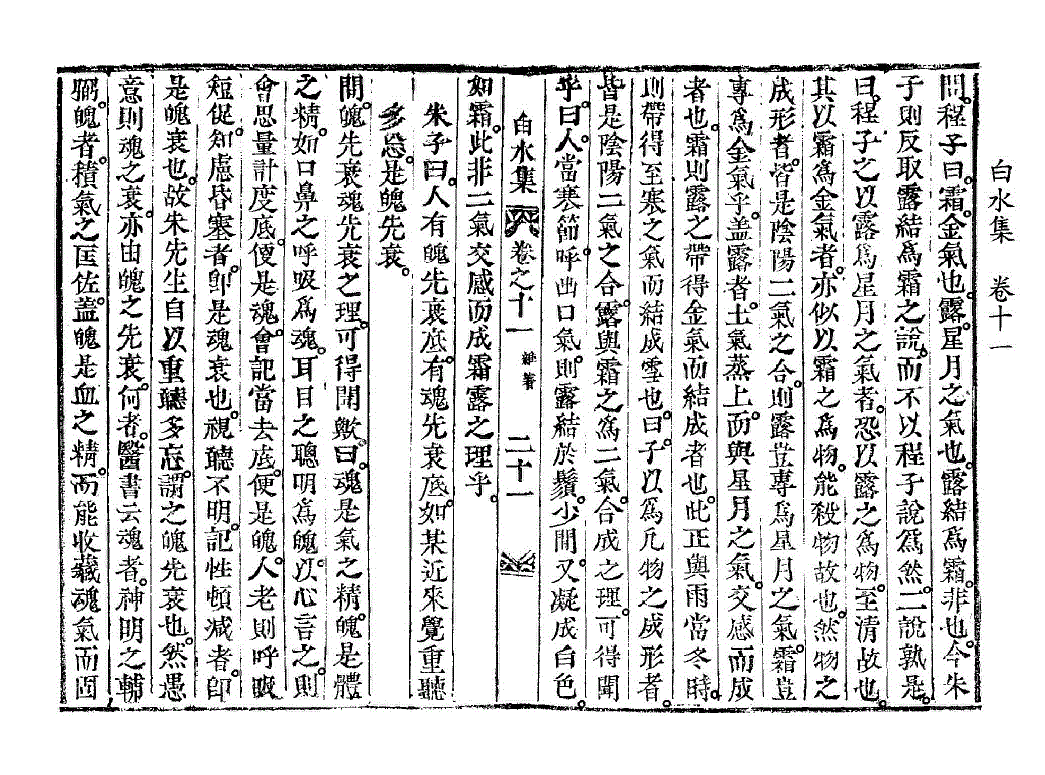 问。程子曰。霜。金气也。露。星月之气也。露结为霜。非也。今朱子则反取露结为霜之说。而不以程子说为然。二说孰是。曰。程子之以露为星月之气者。恐以露之为物。至清故也。其以霜为金气者。亦似以霜之为物。能杀物故也。然物之成形者。皆是阴阳二气之合。则露岂专为星月之气。霜岂专为金气乎。盖露者。土气蒸上。而与星月之气。交感而成者也。霜则露之带得金气而结成者也。此正与雨当冬时。则带得至寒之气而结成雪也。曰。子以为凡物之成形者。皆是阴阳二气之合。露与霜之为二气。合成之理。可得闻乎。曰。人当寒节。呼出口气。则露结于须。少间。又凝成白色。如霜。此非二气交感而成霜露之理乎。
问。程子曰。霜。金气也。露。星月之气也。露结为霜。非也。今朱子则反取露结为霜之说。而不以程子说为然。二说孰是。曰。程子之以露为星月之气者。恐以露之为物。至清故也。其以霜为金气者。亦似以霜之为物。能杀物故也。然物之成形者。皆是阴阳二气之合。则露岂专为星月之气。霜岂专为金气乎。盖露者。土气蒸上。而与星月之气。交感而成者也。霜则露之带得金气而结成者也。此正与雨当冬时。则带得至寒之气而结成雪也。曰。子以为凡物之成形者。皆是阴阳二气之合。露与霜之为二气。合成之理。可得闻乎。曰。人当寒节。呼出口气。则露结于须。少间。又凝成白色。如霜。此非二气交感而成霜露之理乎。朱子曰。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来觉重听多忘。是魄先衰。
问。魄先衰魂先衰之理。可得闻欤。曰。魂是气之精。魄是体之精。如口鼻之呼吸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以心言之。则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人老则呼吸短促。知虑昏塞者。即是魂衰也。视听不明。记性顿减者。即是魄衰也。故朱先生自以重听多忘。谓之魄先衰也。然愚意则魂之衰。亦由魄之先衰。何者。医书云魂者。神明之辅弼。魄者。积气之匡佐。盖魄是血之精。而能收藏魂气而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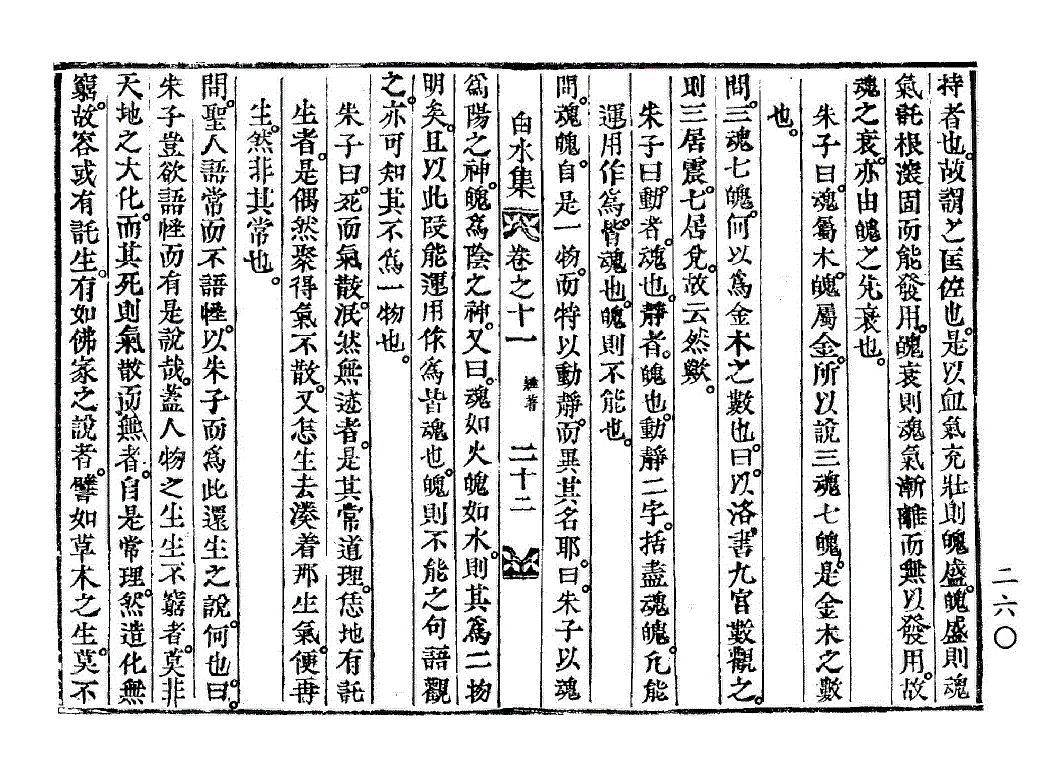 持者也。故谓之匡佐也。是以血气充壮则魄盛。魄盛则魂气托根深固而能发用。魄衰则魂气渐离而无以发用。故魂之衰。亦由魄之先衰也。
持者也。故谓之匡佐也。是以血气充壮则魄盛。魄盛则魂气托根深固而能发用。魄衰则魂气渐离而无以发用。故魂之衰。亦由魄之先衰也。朱子曰。魂属木。魄属金。所以说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数也。
问。三魂七魄。何以为金木之数也。曰。以洛书九宫数观之。则三居震。七居兑。故云然欤。
朱子曰。动者。魂也。静者。魄也。动静二字。括尽魂魄。凡能运用作为。皆魂也。魄则不能也。
问。魂魄。自是一物。而特以动静。而异其名耶。曰。朱子以魂为阳之神。魄为阴之神。又曰。魂如火魄如水。则其为二物明矣。且以此段能运用作为皆魂也。魄则不能之句语观之。亦可知其不为一物也。
朱子曰。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怎生去凑着那生气。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问。圣人语常而不语怪。以朱子而为此还生之说。何也。曰。朱子岂欲语怪而有是说哉。盖人物之生生不穷者。莫非天地之大化。而其死则气散而无者。自是常理。然造化无穷。故容或有托生。有如佛家之说者。譬如草木之生。莫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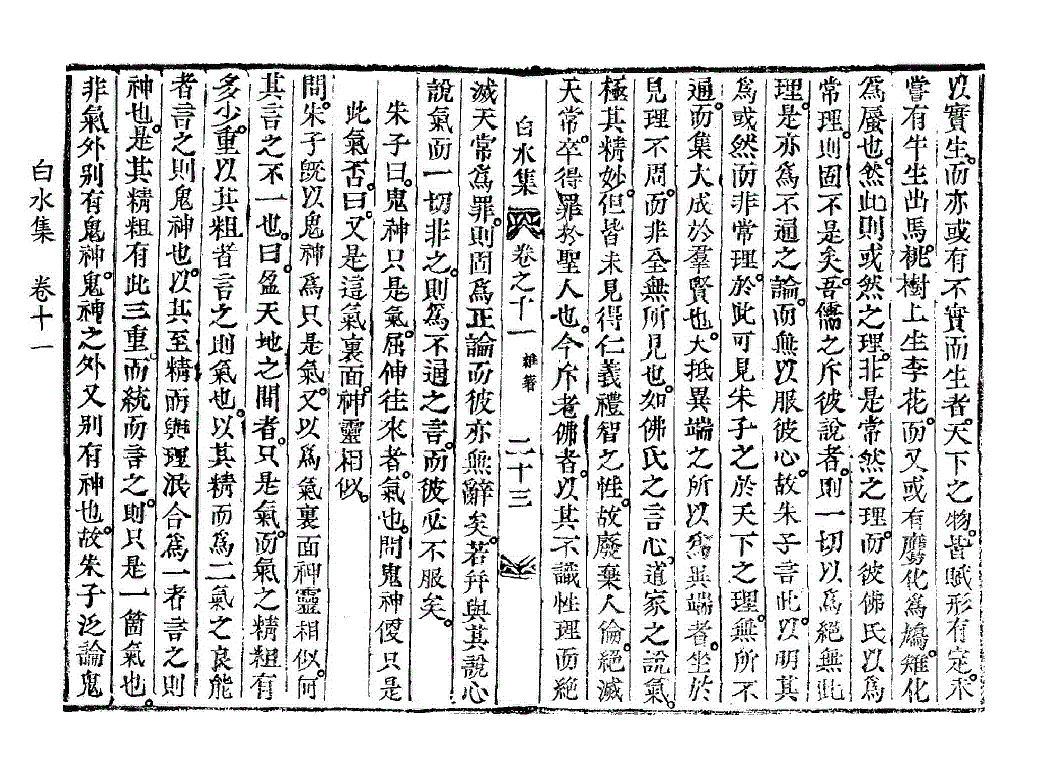 以实生。而亦或有不实而生者。天下之物。皆赋形有定。未尝有牛生出马。桃树上生李花。而又或有鹰化为鸠。雉化为蜃也。然此则或然之理。非是常然之理。而彼佛氏以为常理。则固不是矣。吾儒之斥彼说者。则一切以为绝无此理。是亦为不通之论。而无以服彼心。故朱子言此。以明其为或然而非常理。于此可见朱子之于天下之理。无所不通。而集大成于群贤也。大抵异端之所以为异端者。坐于见理不周。而非全无所见也。如佛氏之言心。道家之说气。极其精妙。但皆未见得仁义礼智之性。故废弃人伦。绝灭天常。卒得罪于圣人也。今斥老佛者。以其不识性理而绝灭天常为罪。则固为正论而彼亦无辞矣。若并与其说心说气而一切非之。则为不通之言。而彼必不服矣。
以实生。而亦或有不实而生者。天下之物。皆赋形有定。未尝有牛生出马。桃树上生李花。而又或有鹰化为鸠。雉化为蜃也。然此则或然之理。非是常然之理。而彼佛氏以为常理。则固不是矣。吾儒之斥彼说者。则一切以为绝无此理。是亦为不通之论。而无以服彼心。故朱子言此。以明其为或然而非常理。于此可见朱子之于天下之理。无所不通。而集大成于群贤也。大抵异端之所以为异端者。坐于见理不周。而非全无所见也。如佛氏之言心。道家之说气。极其精妙。但皆未见得仁义礼智之性。故废弃人伦。绝灭天常。卒得罪于圣人也。今斥老佛者。以其不识性理而绝灭天常为罪。则固为正论而彼亦无辞矣。若并与其说心说气而一切非之。则为不通之言。而彼必不服矣。朱子曰。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问鬼神便只是此气否。曰。又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
问。朱子既以鬼神为只是气。又以为气里面神灵相似。何其言之不一也。曰。盈天地之间者。只是气。而气之精粗有多少。重以其粗者言之则气也。以其精而为二气之良能者言之则鬼神也。以其至精而与理泯合为一者言之则神也。是其精粗有此三重。而统而言之。则只是一个气也。非气外别有鬼神。鬼神之外又别有神也。故朱子泛论鬼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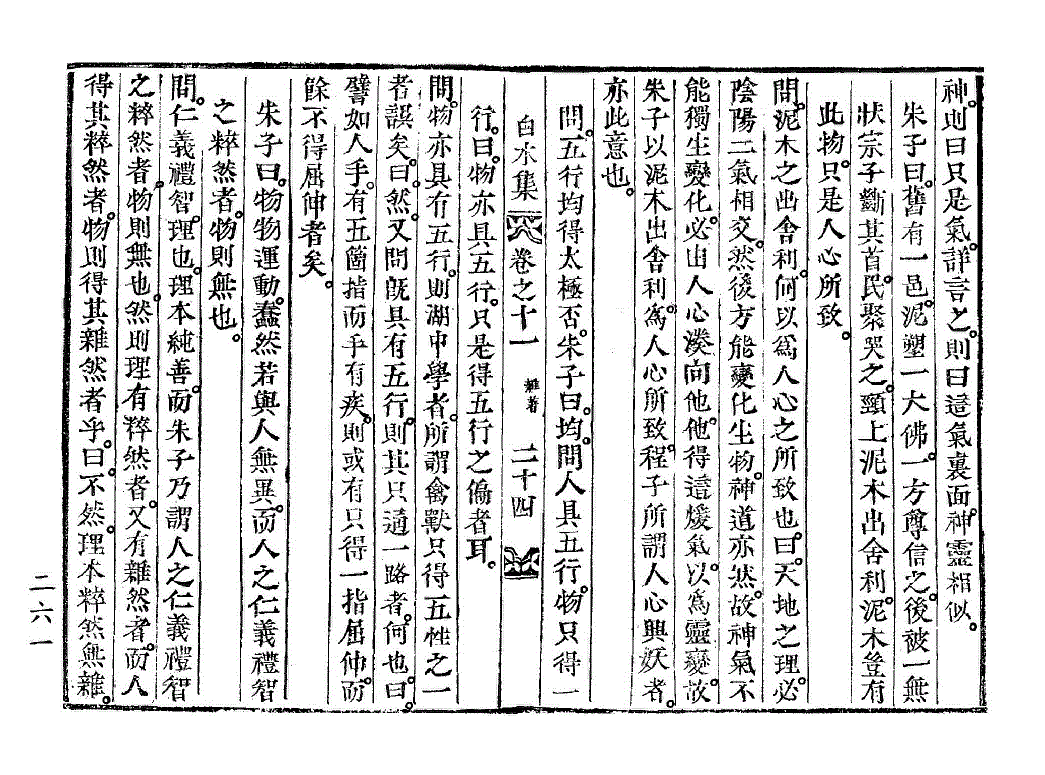 神。则曰只是气。详言之。则曰这气里面。神灵相似。
神。则曰只是气。详言之。则曰这气里面。神灵相似。朱子曰。旧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后被一无状宗子断其首。民聚哭之。颈上泥木出舍利。泥木岂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问。泥木之出舍利。何以为人心之所致也。曰。天地之理。必阴阳二气相交。然后方能变化生物。神道亦然。故神气不能独生变化。必由人心凑向他。他得这煖气。以为灵变。故朱子以泥木出舍利。为人心所致。程子所谓人心兴妖者。亦此意也。
问。五行均得太极否。朱子曰。均。问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
问。物亦具有五行。则湖中学者。所谓禽兽只得五性之一者误矣。曰。然。又问既具有五行。则其只通一路者。何也。曰。譬如人手。有五个指而手有疾。则或有只得一指屈伸。而馀不得屈伸者矣。
朱子曰。物物运动。蠢然若与人无异。而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
问。仁义礼智。理也。理本纯善。而朱子乃谓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然则理有粹然者。又有杂然者。而人得其粹然者。物则得其杂然者乎。曰。不然。理本粹然无杂。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2H 页
 而人则禀得清秀之气。故其粹然者。全体呈露。物则禀得浊驳偏塞之气。故其粹然之体。为其所蔽而不得著见。故曰。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此譬如宝珠在清水之中。则其光明之全体尽见。而若在污泥之中。则无以见其光明之本体也。今谓清水之宝珠光明。在污泥则无也则可。若曰宝珠有粹然者。有杂然者。清水得其粹然者。污泥得其杂然者云尔则可乎。
而人则禀得清秀之气。故其粹然者。全体呈露。物则禀得浊驳偏塞之气。故其粹然之体。为其所蔽而不得著见。故曰。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此譬如宝珠在清水之中。则其光明之全体尽见。而若在污泥之中。则无以见其光明之本体也。今谓清水之宝珠光明。在污泥则无也则可。若曰宝珠有粹然者。有杂然者。清水得其粹然者。污泥得其杂然者云尔则可乎。问。尧舜之气。常清明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朱子曰。气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气。有时而清明。尧舜之气。无时而昏浊。先生答之不详。次日廖再问。恐是天地之气。一时如此。曰。天地之气。与物相通。只得从人躯壳里过来。
问。以尧舜而生丹朱商均。以瞽瞍而生大舜之理。虽有此语类问答。而未能晓然。愿闻明教。曰。人物之生。其气质自有定种。然一人之所生。而其智愚贤不肖。各各不同者。以其化生之初。外感之气。有万不齐故也。盖天地间游气流行。变动无常。或有清明之时。或有昏暗之时。人生始化之际。适值天气清明之时。则虽以瞽瞍之气质。而感得天地清明之气。能生大舜之圣。适值天气昏暗之时。则虽以尧舜之气质。而感得天地昏暗之气。便生朱均之不肖。谚云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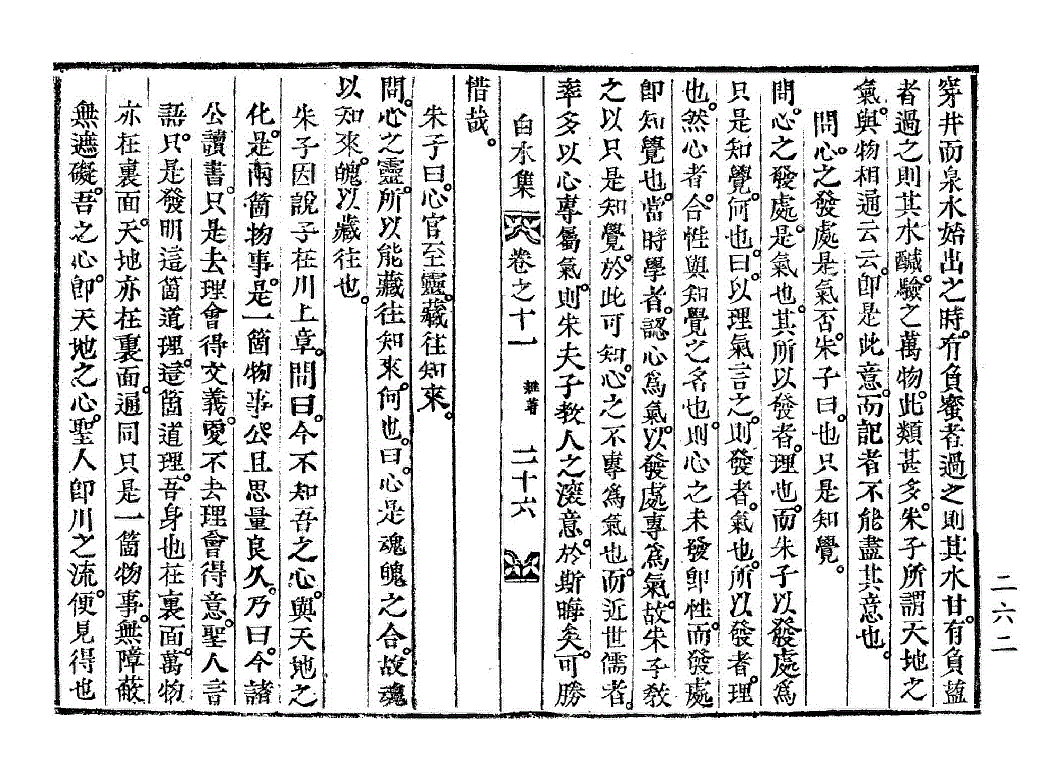 穿井而泉水始出之时。有负蜜者过之则其水甘。有负盐者过之则其水咸。验之万物。此类甚多。朱子所谓天地之气。与物相通云云。即是此意。而记者不能尽其意也。
穿井而泉水始出之时。有负蜜者过之则其水甘。有负盐者过之则其水咸。验之万物。此类甚多。朱子所谓天地之气。与物相通云云。即是此意。而记者不能尽其意也。问。心之发处是气否。朱子曰。也只是知觉。
问。心之发处。是气也。其所以发者。理也。而朱子以发处为只是知觉。何也。曰。以理气言之。则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然心者。合性与知觉之名也。则心之未发即性。而发处即知觉也。当时学者。认心为气。以发处专为气。故朱子教之以只是知觉。于此可知。心之不专为气也。而近世儒者。率多以心专属气。则朱夫子教人之深意。于斯晦矣。可胜惜哉。
朱子曰。心官至灵。藏往知来。
问。心之灵。所以能藏往知来。何也。曰。心是魂魄之合。故魂以知来。魄以藏往也。
朱子因说子在川上章。问曰。今不知吾之心。与天地之化。是两个物事。是一个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诸公读书。只是去理会得文义。更不去理会得意。圣人言语。只是发明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吾身也在里面。万物亦在里面。天地亦在里面。通同只是一个物事。无障蔽无遮碍。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圣人即川之流。便见得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3H 页
 是此理无往而非极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与天地不相似。而今讲学。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
是此理无往而非极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与天地不相似。而今讲学。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问。朱子于此上段。则曰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于下段。则曰天命至正。人心便邪。天命至公。人心便私。天命至大。人心便小。所以与天地不相似。而今讲学。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敢问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者。何心也。与天地不相似者。又何心也。岂一人之身。有二心耶。曰。非心有二也。心则一。而心之气有二。故云然也。程子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为心。其用则谓之神。在人为情。所谓其体其用。即是在天本然之神气也。是则易所谓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也。今此语类上段。通同只是一个物事。及天命至正至公至大者。此之谓也。朱子又论人心道心曰。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盖人生成形之后。天赋本然之神气。与血气交合。以生知觉。故知觉或从义理上发。或从人欲上发。从义理而发者为道心。此则由于本然之气也。从人欲而发者为人心。此则生于血气也。今此语类下段所谓人心便邪便私便小。与天地不相似者。指其生于血气者而言也。其曰而今讲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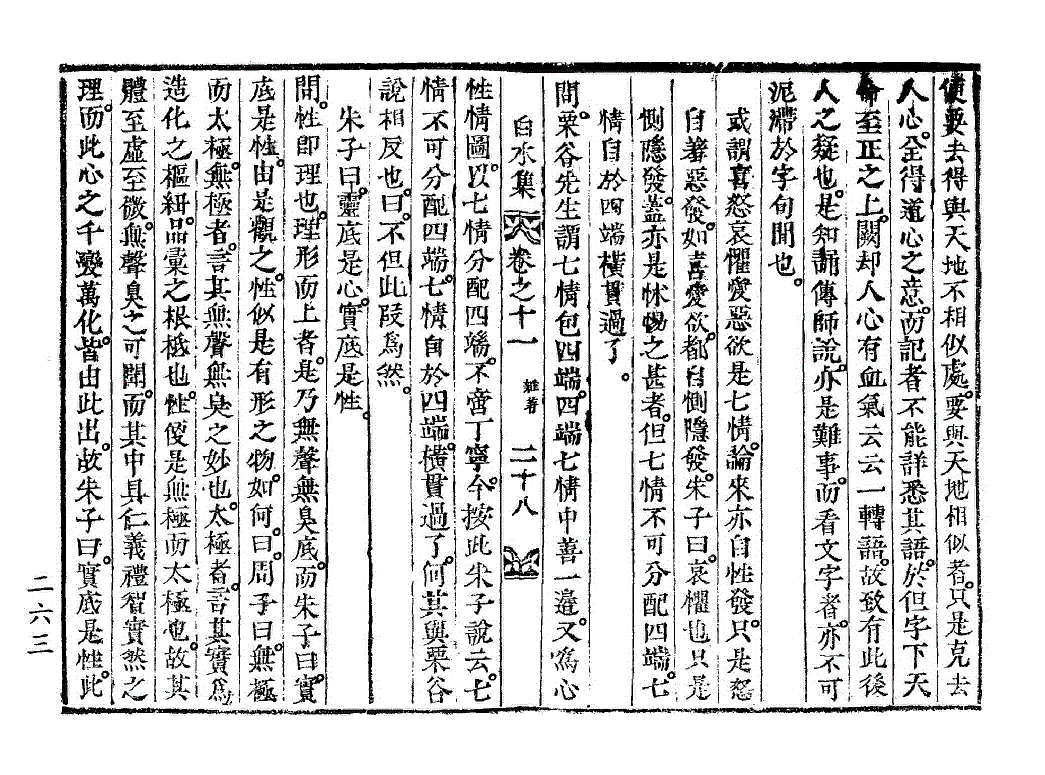 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者。只是克去人心。全得道心之意。而记者不能详悉其语。于但字下天命至正之上。阙却人心有血气云云一转语。故致有此后人之疑也。是知诵传师说。亦是难事。而看文字者。亦不可泥滞于字句间也。
便要去得与天地不相似处。要与天地相似者。只是克去人心。全得道心之意。而记者不能详悉其语。于但字下天命至正之上。阙却人心有血气云云一转语。故致有此后人之疑也。是知诵传师说。亦是难事。而看文字者。亦不可泥滞于字句间也。或谓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七情。论来亦自性发。只是怒自羞恶发。如喜爱欲。都自恻隐发。朱子曰。哀惧也只是恻隐发。盖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
问。栗谷先生谓七情包四端。四端七情中善一边。又为心性情图。以七情分配四端。不啻丁宁。今按此朱子说云。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何其与栗谷说相反也。曰。不但此段为然。
朱子曰。灵底是心。实底是性。
问。性即理也。理形而上者。是乃无声无臭底。而朱子曰。实底是性。由是观之。性似是有形之物。如何。曰。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无极者。言其无声无臭之妙也。太极者。言其实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性便是无极而太极也。故其体至虚至微。无声臭之可闻。而其中具仁义礼智实然之理。而此心之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故朱子曰。实底是性。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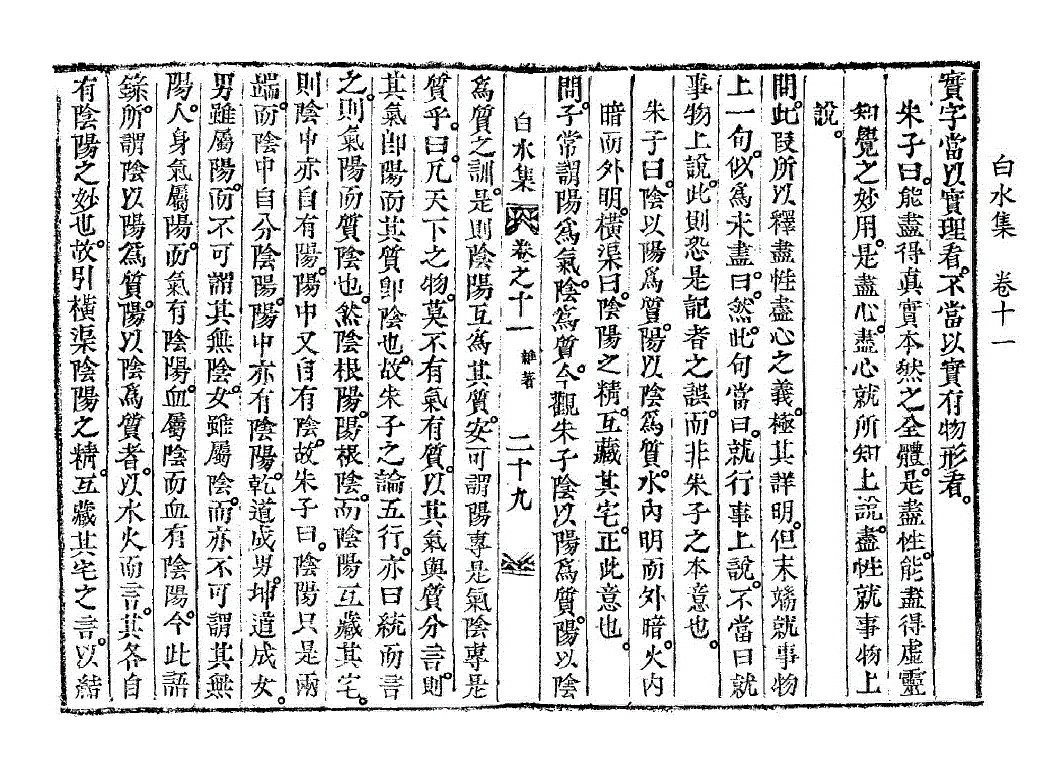 实字当以实理看。不当以实有物形看。
实字当以实理看。不当以实有物形看。朱子曰。能尽得真实本然之全体。是尽性。能尽得虚灵知觉之妙用。是尽心。尽心就所知上说。尽性就事物上说。
问。此段所以释尽性尽心之义。极其详明。但末端就事物上一句。似为未尽。曰。然。此句当曰。就行事上说。不当曰就事物上说。此则恐是记者之误。而非朱子之本意也。
朱子曰。阴以阳为质。阳以阴为质。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明。横渠曰。阴阳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问。子常谓阳为气。阴为质。今观朱子阴以阳为质。阳以阴为质之训。是则阴阳互为其质。安可谓阳专是气阴专是质乎。曰。凡天下之物。莫不有气有质。以其气与质分言。则其气即阳而其质即阴也。故朱子之论五行。亦曰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然阴根阳。阳根阴。而阴阳互藏其宅。则阴中亦自有阳。阳中又自有阴。故朱子曰。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虽属阳。而不可谓其无阴。女虽属阴。而亦不可谓其无阳。人身气属阳。而气有阴阳。血属阴而血有阴阳。今此语录。所谓阴以阳为质。阳以阴为质者。以水火而言。其各自有阴阳之妙也。故引横渠阴阳之精。互藏其宅之言。以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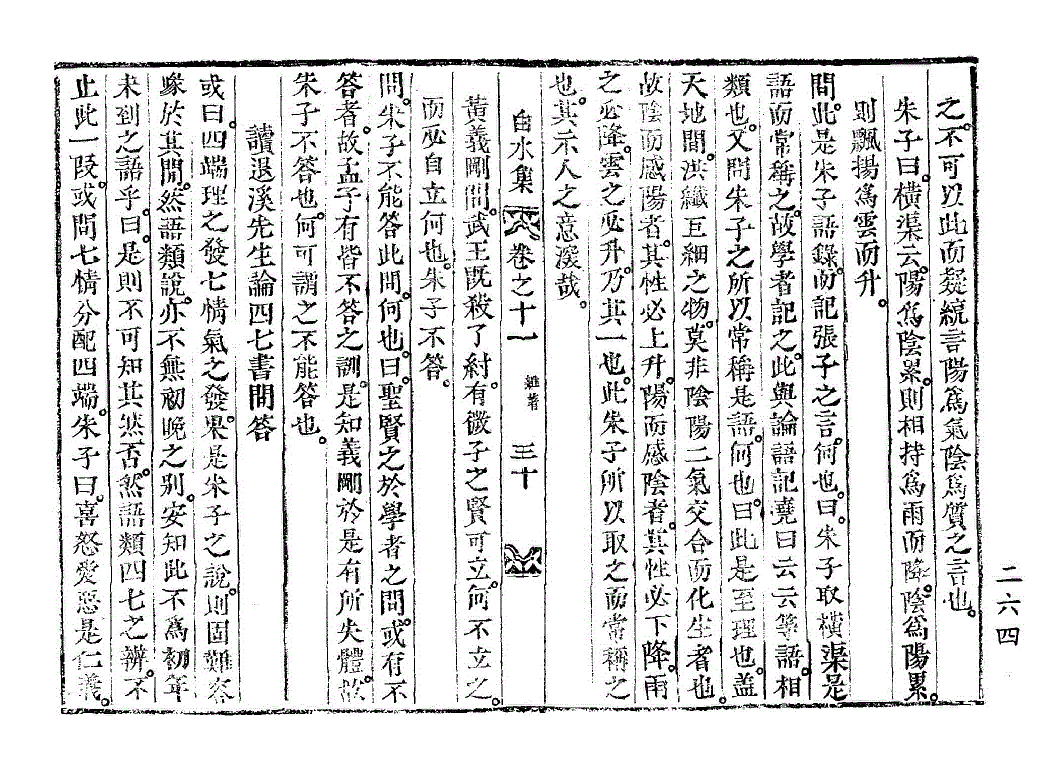 之。不可以此而疑统言阳为气阴为质之言也。
之。不可以此而疑统言阳为气阴为质之言也。朱子曰。横渠云。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累。则飘扬为云而升。
问。此是朱子语录。而记张子之言。何也。曰。朱子取横渠是语而常称之。故学者记之。此与论语记尧曰云云等语。相类也。又问朱子之所以常称是语。何也。曰此是至理也。盖天地间。洪纤巨细之物。莫非阴阳二气交合而化生者也。故阴而感阳者。其性必上升。阳而感阴者。其性必下降。雨之必降。云之必升。乃其一也。此朱子所以取之而常称之也。其示人之意深哉。
黄义刚问。武王既杀了纣。有微子之贤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朱子不答。
问。朱子不能答此问。何也。曰。圣贤之于学者之问。或有不答者。故孟子有皆不答之训。是知义刚于是有所失体。故朱子不答也。何可谓之不能答也。
读退溪先生论四七书问答
或曰。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果是朱子之说。则固难容喙于其閒。然语类说。亦不无初晚之别。安知此不为初年未到之语乎。曰。是则不可知其然否。然语类四七之辨。不止此一段。或问七情分配四端。朱子曰。喜怒爱恶是仁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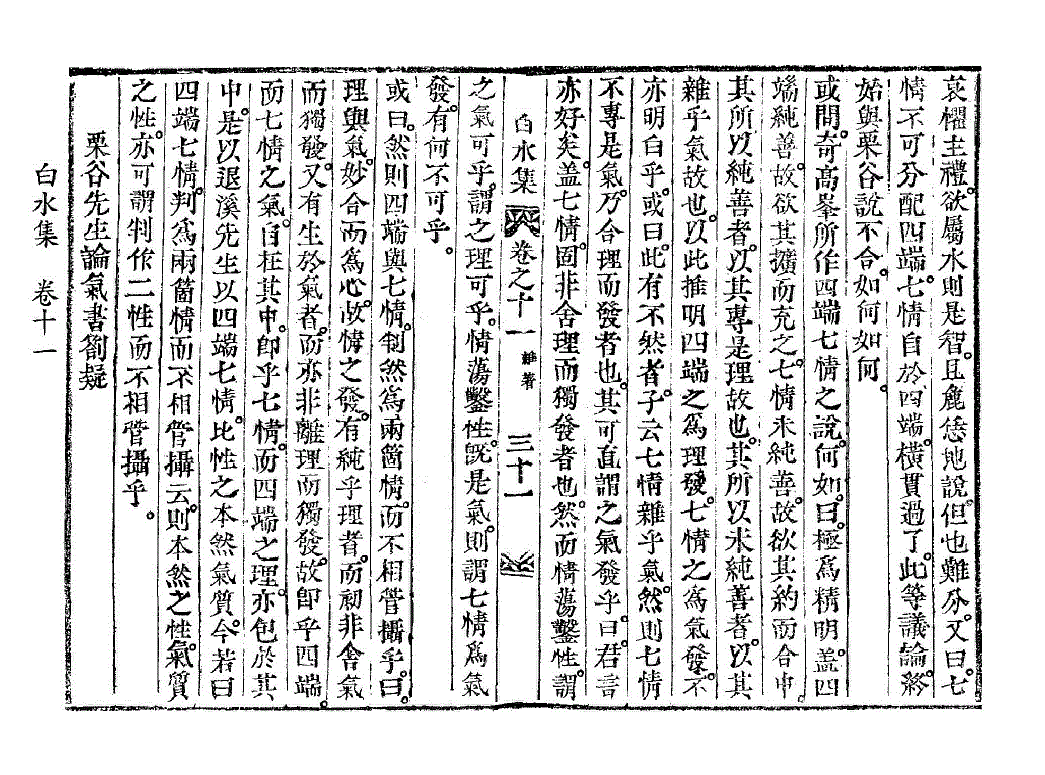 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此等议论。终始与栗谷说不合。如何如何。
哀惧主礼。欲属水则是智。且粗恁地说。但也难分。又曰。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于四端。横贯过了。此等议论。终始与栗谷说不合。如何如何。或问。奇高峰所作四端七情之说。何如。曰。极为精明。盖四端纯善。故欲其扩而充之。七情未纯善。故欲其约而合中。其所以纯善者。以其专是理故也。其所以未纯善者。以其杂乎气故也。以此推明四端之为理发。七情之为气发。不亦明白乎。或曰。此有不然者。子云七情杂乎气。然则七情不专是气。乃合理而发者也。其可直谓之气发乎。曰。君言亦好矣。盖七情。固非舍理而独发者也。然而情荡凿性。谓之气可乎。谓之理可乎。情荡凿性。既是气。则谓七情为气发。有何不可乎。
或曰。然则四端与七情。判然为两个情。而不相管摄乎。曰。理与气。妙合而为心。故情之发。有纯乎理者。而初非舍气而独发。又有生于气者。而亦非离理而独发。故即乎四端。而七情之气。自在其中。即乎七情。而四端之理。亦包于其中。是以退溪先生以四端七情。比性之本然气质。今若曰四端七情。判为两个情而不相管摄云。则本然之性。气质之性。亦可谓判作二性而不相管摄乎。
栗谷先生论气书劄疑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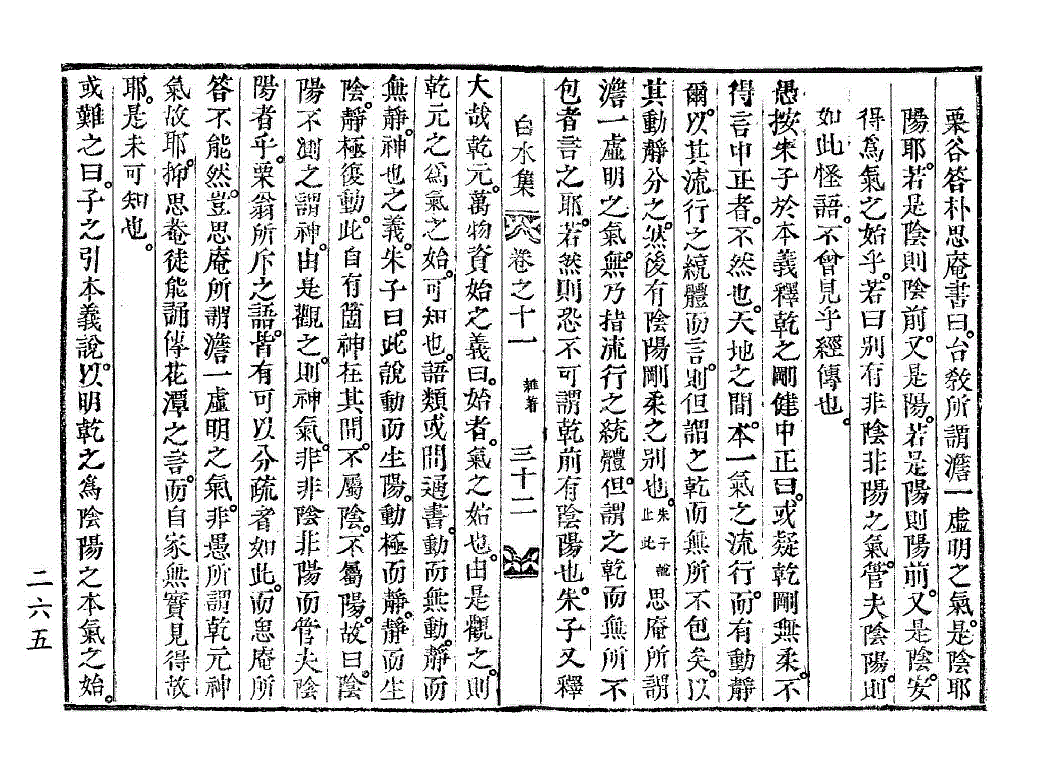 栗谷答朴思庵书曰。台教所谓澹一虚明之气。是阴耶阳耶。若是阴则阴前。又是阳。若是阳则阳前。又是阴。安得为气之始乎。若曰别有非阴非阳之气。管夫阴阳。则如此怪语。不曾见乎经传也。
栗谷答朴思庵书曰。台教所谓澹一虚明之气。是阴耶阳耶。若是阴则阴前。又是阳。若是阳则阳前。又是阴。安得为气之始乎。若曰别有非阴非阳之气。管夫阴阳。则如此怪语。不曾见乎经传也。愚按朱子于本义释乾之刚健中正曰。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朱子说止此)思庵所谓澹一虚明之气。无乃指流行之统体。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者言之耶。若然则恐不可谓乾前有阴阳也。朱子又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义曰。始者。气之始也。由是观之。则乾元之为气之始。可知也。语类或问通书。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义。朱子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是观之。则神气。非非阴非阳而管夫阴阳者乎。栗翁所斥之语。皆有可以分疏者如此。而思庵所答不能然。岂思庵所谓澹一虚明之气。非愚所谓乾元神气故耶。抑思庵徒能诵传花潭之言。而自家无实见得故耶。是未可知也。
或难之曰。子之引本义说。以明乾之为阴阳之本气之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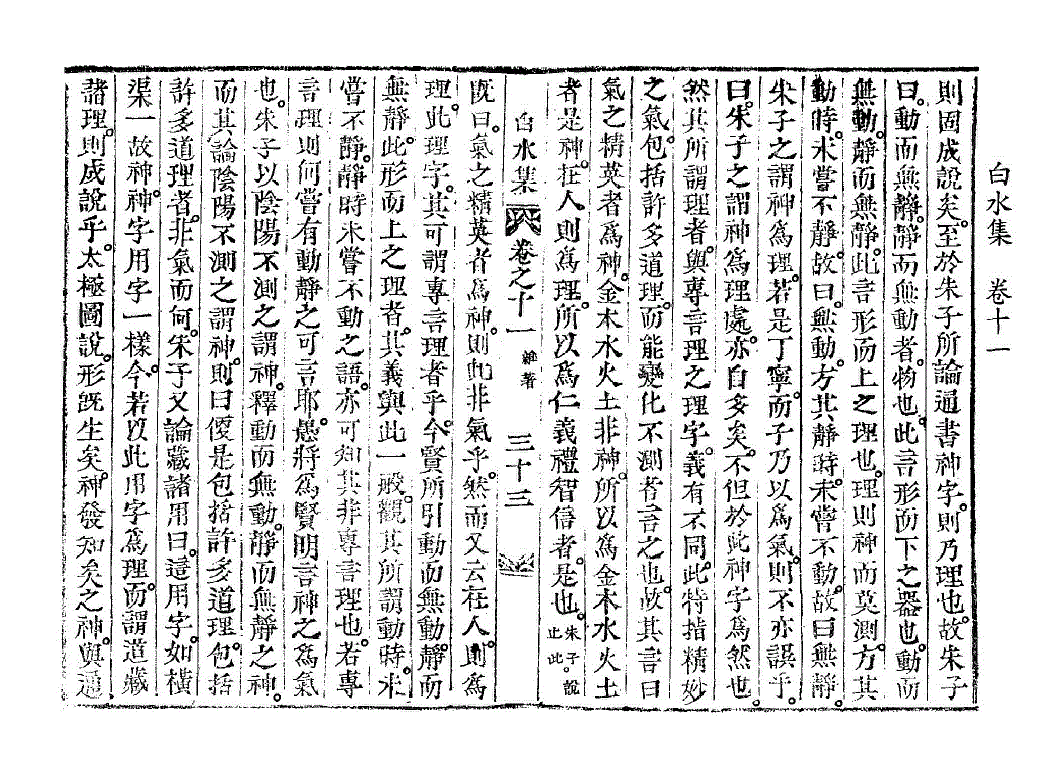 则固成说矣。至于朱子所论通书神字。则乃理也。故朱子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朱子之谓神为理。若是丁宁。而子乃以为气。则不亦误乎。曰。朱子之谓神为理处。亦自多矣。不但于此神字为然也。然其所谓理者。与专言理之理字。义有不同。此特指精妙之气。包括许多道理。而能变化不测者言之也。故其言曰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朱子说止此。)既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则此非气乎。然而又云在人。则为理。此理字。其可谓专言理者乎。今贤所引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形而上之理者。其义与此一般。观其所谓动时。未尝不静。静时未尝不动之语。亦可知其非专言理也。若专言理则何尝有动静之可言耶。愚将为贤明言神之为气也。朱子以阴阳不测之谓神。释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神。而其论阴阳不测之谓神。则曰便是包括许多道理。包括许多道理者。非气而何。朱子又论藏诸用曰。这用字。如横渠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样。今若以此用字为理。而谓道藏诸理。则成说乎。太极图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神。与通
则固成说矣。至于朱子所论通书神字。则乃理也。故朱子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朱子之谓神为理。若是丁宁。而子乃以为气。则不亦误乎。曰。朱子之谓神为理处。亦自多矣。不但于此神字为然也。然其所谓理者。与专言理之理字。义有不同。此特指精妙之气。包括许多道理。而能变化不测者言之也。故其言曰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朱子说止此。)既曰。气之精英者为神。则此非气乎。然而又云在人。则为理。此理字。其可谓专言理者乎。今贤所引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此形而上之理者。其义与此一般。观其所谓动时。未尝不静。静时未尝不动之语。亦可知其非专言理也。若专言理则何尝有动静之可言耶。愚将为贤明言神之为气也。朱子以阴阳不测之谓神。释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之神。而其论阴阳不测之谓神。则曰便是包括许多道理。包括许多道理者。非气而何。朱子又论藏诸用曰。这用字。如横渠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样。今若以此用字为理。而谓道藏诸理。则成说乎。太极图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神。与通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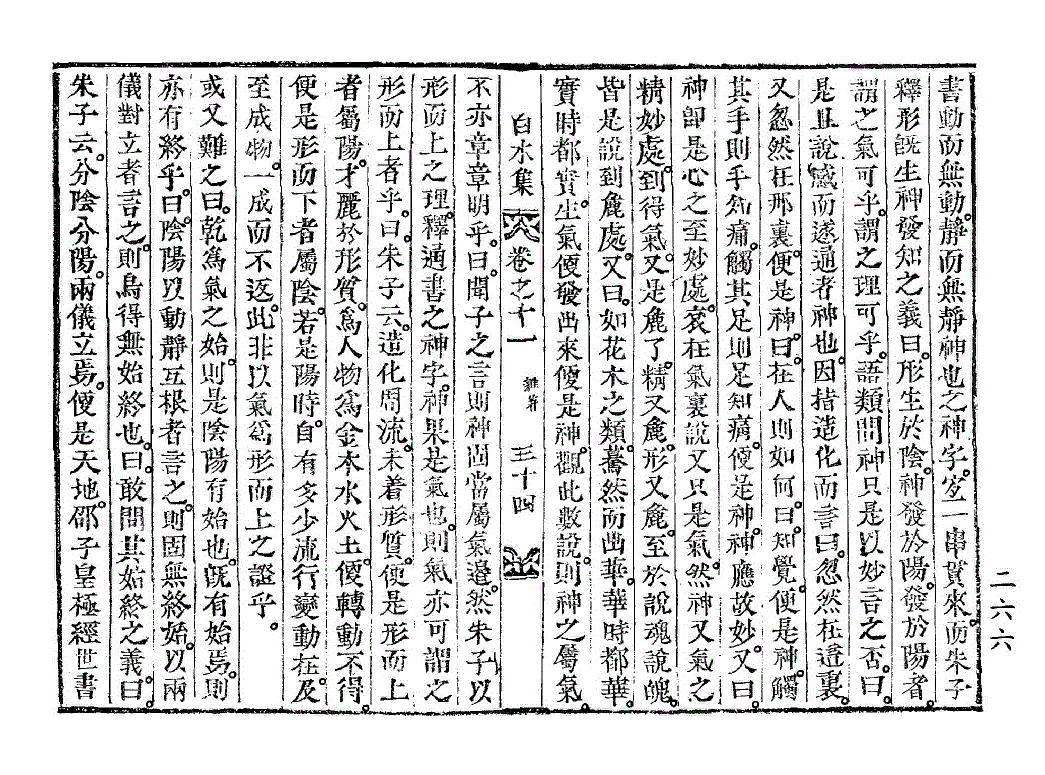 书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神字。宜一串贯来。而朱子释形既生神发知之义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发于阳者。谓之气可乎。谓之理可乎。语类问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说感而遂通者神也。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这里。又忽然在那里。便是神。曰。在人则如何。曰。知觉。便是神。触其手则手知痛。触其足则足知痛。便是神。神应故妙。又曰。神即是心之至妙处。衮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又曰。如花木之类。蓦然而出华。华时都华。实时都实。生气便发出来便是神。观此数说。则神之属气。不亦章章明乎。曰。闻子之言则神固当属气边。然朱子以形而上之理。释通书之神字。神果是气也。则气亦可谓之形而上者乎。曰。朱子云。造化周流。未着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此非以气为形而上之證乎。
书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之神字。宜一串贯来。而朱子释形既生神发知之义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发于阳者。谓之气可乎。谓之理可乎。语类问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说感而遂通者神也。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这里。又忽然在那里。便是神。曰。在人则如何。曰。知觉。便是神。触其手则手知痛。触其足则足知痛。便是神。神应故妙。又曰。神即是心之至妙处。衮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气之精妙处。到得气。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于说魂说魄。皆是说到粗处。又曰。如花木之类。蓦然而出华。华时都华。实时都实。生气便发出来便是神。观此数说。则神之属气。不亦章章明乎。曰。闻子之言则神固当属气边。然朱子以形而上之理。释通书之神字。神果是气也。则气亦可谓之形而上者乎。曰。朱子云。造化周流。未着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此非以气为形而上之證乎。或又难之曰。乾为气之始。则是阴阳有始也。既有始焉。则亦有终乎。曰。阴阳以动静互根者言之。则固无终始。以两仪对立者言之。则乌得无始终也。曰。敢问其始终之义。曰。朱子云。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便是天地。邵子皇极经世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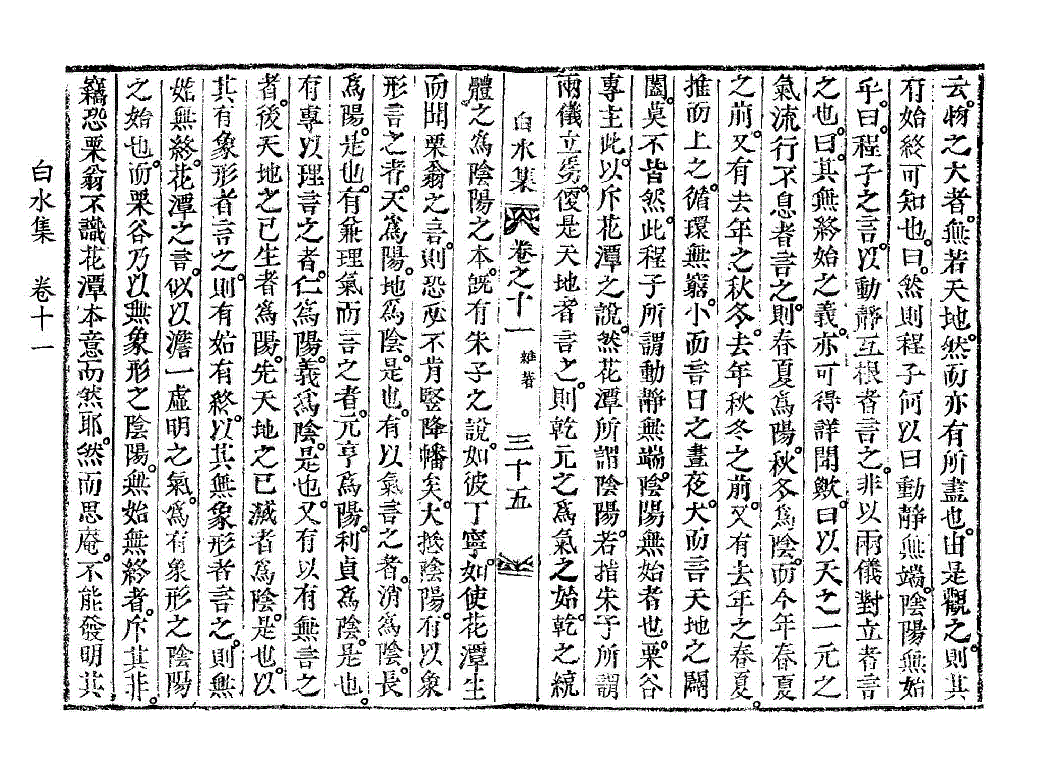 云。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由是观之。则其有始终可知也。曰。然则程子何以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乎。曰。程子之言。以动静互根者言之。非以两仪对立者言之也。曰。其无终始之义。亦可得详闻欤。曰以天之一元之气流行不息者言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而今年春夏之前。又有去年之秋冬。去年秋冬之前。又有去年之春夏。推而上之。循环无穷。小而言日之昼夜。大而言天地之辟阖。莫不皆然。此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也。栗谷专主此。以斥花潭之说。然花潭所谓阴阳。若指朱子所谓两仪立焉。便是天地者言之。则乾元之为气之始。乾之统体之为阴阳之本。既有朱子之说。如彼丁宁。如使花潭生而闻栗翁之言。则恐必不肯竖降幡矣。大抵阴阳。有以象形言之者。天为阳。地为阴。是也。有以气言之者。消为阴。长为阳。是也。有兼理气而言之者。元亨为阳。利贞为阴。是也。有专以理言之者。仁为阳。义为阴。是也。又有以有无言之者。后天地之已生者为阳。先天地之已灭者为阴。是也。以其有象形者言之。则有始有终。以其无象形者言之。则无始无终。花潭之言。似以澹一虚明之气。为有象形之阴阳之始也。而栗谷乃以无象形之阴阳。无始无终者。斥其非。窃恐栗翁不识花潭本意而然耶。然而思庵。不能发明其
云。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由是观之。则其有始终可知也。曰。然则程子何以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乎。曰。程子之言。以动静互根者言之。非以两仪对立者言之也。曰。其无终始之义。亦可得详闻欤。曰以天之一元之气流行不息者言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而今年春夏之前。又有去年之秋冬。去年秋冬之前。又有去年之春夏。推而上之。循环无穷。小而言日之昼夜。大而言天地之辟阖。莫不皆然。此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也。栗谷专主此。以斥花潭之说。然花潭所谓阴阳。若指朱子所谓两仪立焉。便是天地者言之。则乾元之为气之始。乾之统体之为阴阳之本。既有朱子之说。如彼丁宁。如使花潭生而闻栗翁之言。则恐必不肯竖降幡矣。大抵阴阳。有以象形言之者。天为阳。地为阴。是也。有以气言之者。消为阴。长为阳。是也。有兼理气而言之者。元亨为阳。利贞为阴。是也。有专以理言之者。仁为阳。义为阴。是也。又有以有无言之者。后天地之已生者为阳。先天地之已灭者为阴。是也。以其有象形者言之。则有始有终。以其无象形者言之。则无始无终。花潭之言。似以澹一虚明之气。为有象形之阴阳之始也。而栗谷乃以无象形之阴阳。无始无终者。斥其非。窃恐栗翁不识花潭本意而然耶。然而思庵。不能发明其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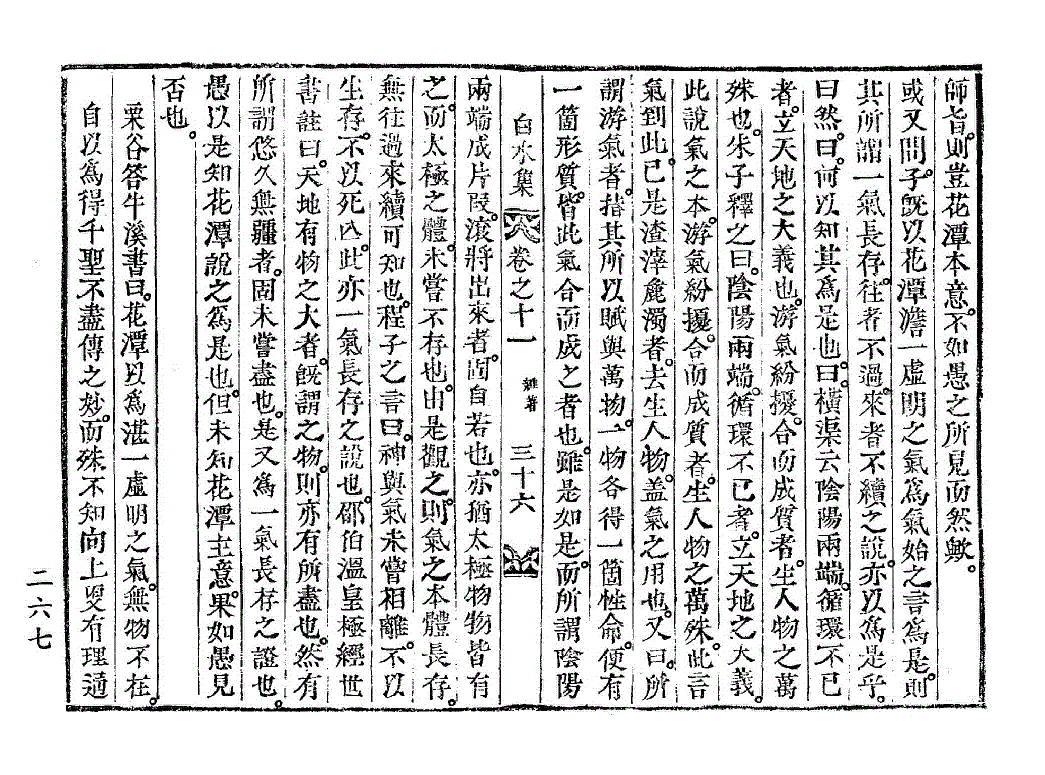 师旨。则岂花潭本意。不如愚之所见而然欤。
师旨。则岂花潭本意。不如愚之所见而然欤。或又问。子既以花潭澹一虚明之气为气始之言为是。则其所谓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之说。亦以为是乎。曰然。曰。何以知其为是也。曰。横渠云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也。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也。朱子释之曰。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此说气之本。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此言气到此。已是渣滓粗浊者。去生人物。盖气之用也。又曰。所谓游气者。指其所以赋与万物。一物各得一个性命。便有一个形质。皆此气合而成之者也。虽是如是。而所谓阴阳两端成片段。滚将出来者。固自若也。亦犹太极物物皆有之。而太极之体。未尝不存也。由是观之。则气之本体长存。无往过来续可知也。程子之言曰。神与气未尝相离。不以生存。不以死亡。此亦一气长存之说也。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注曰。天地有物之大者。既谓之物。则亦有所尽也。然有所谓悠久无疆者。固未尝尽也。是又为一气长存之證也。愚以是知花潭说之为是也。但未知花潭主意。果如愚见否也。
栗谷答牛溪书曰。花潭以为湛一虚明之气。无物不在。自以为得千圣不尽传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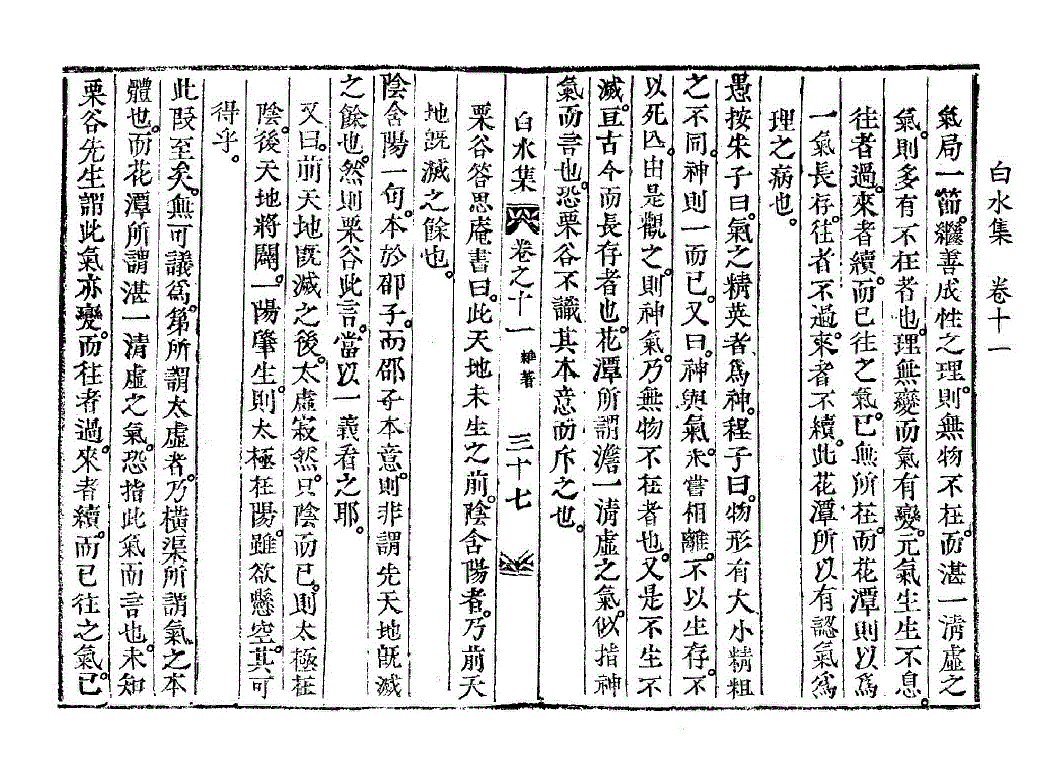 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
气局一节。继善成性之理。则无物不在。而湛一清虚之气。则多有不在者也。理无变而气有变。元气生生不息。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在。而花潭则以为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此花潭所以有认气为理之病也。愚按朱子曰。气之精英者为神。程子曰。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则一而已。又曰。神与气。未尝相离。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由是观之。则神气。乃无物不在者也。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今而长存者也。花潭所谓澹一清虚之气。似指神气而言也。恐栗谷不识其本意而斥之也。
栗谷答思庵书曰。此天地未生之前。阴含阳者。乃前天地既灭之馀也。
阴含阳一句。本于邵子。而邵子本意。则非谓先天地既灭之馀也。然则栗谷此言。当以一义看之耶。
又曰。前天地既灭之后。太虚寂然。只阴而已。则太极在阴。后天地将辟。一阳肇生。则太极在阳。虽欲悬空。其可得乎。
此段至矣。无可议为。第所谓太虚者。乃横渠所谓气之本体也。而花潭所谓湛一清虚之气。恐指此气而言也。未知栗谷先生谓此气亦变。而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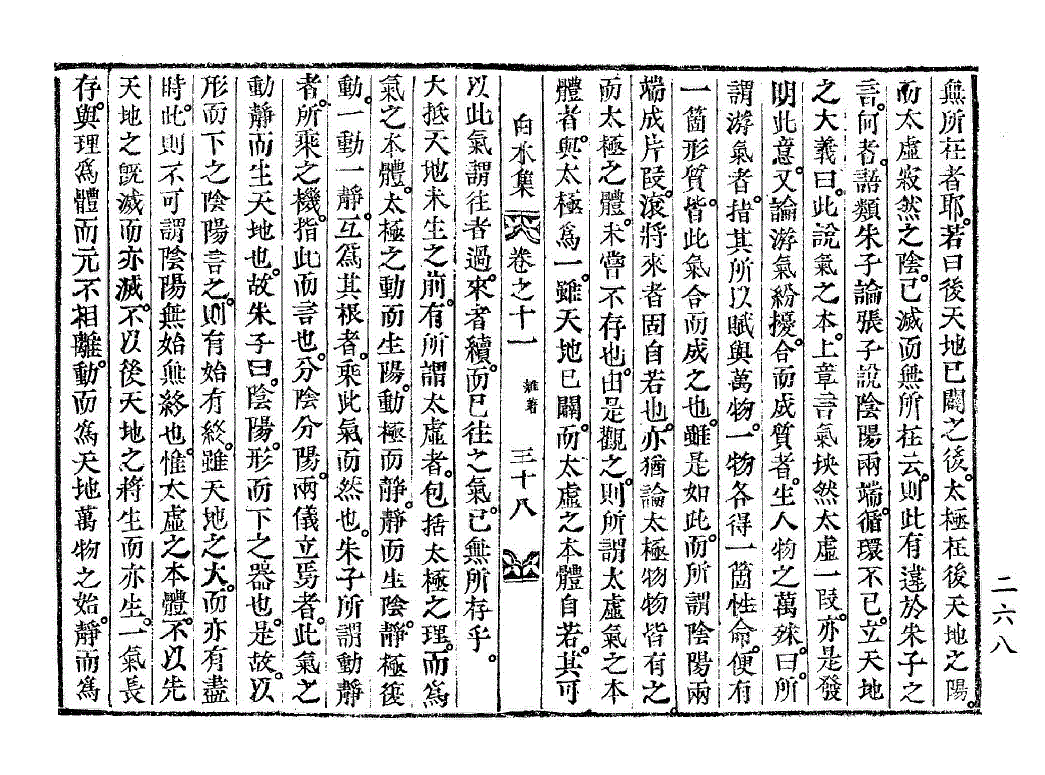 无所在者耶。若曰后天地已辟之后。太极在后天地之阳。而太虚寂然之阴。已灭而无所在云。则此有违于朱子之言。何者。语类朱子论张子说阴阳两端。循环不已。立天地之大义曰。此说气之本。上章言气坱然太虚一段。亦是发明此意。又论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曰。所谓游气者。指其所以赋与万物。一物各得一个性命。便有一个形质。皆此气合而成之也。虽是如此。而所谓阴阳两端成片段。滚将来者固自若也。亦犹论太极物物皆有之。而太极之体。未尝不存也。由是观之。则所谓太虚气之本体者。与太极为一。虽天地已辟。而太虚之本体自若。其可以此气谓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存乎。
无所在者耶。若曰后天地已辟之后。太极在后天地之阳。而太虚寂然之阴。已灭而无所在云。则此有违于朱子之言。何者。语类朱子论张子说阴阳两端。循环不已。立天地之大义曰。此说气之本。上章言气坱然太虚一段。亦是发明此意。又论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曰。所谓游气者。指其所以赋与万物。一物各得一个性命。便有一个形质。皆此气合而成之也。虽是如此。而所谓阴阳两端成片段。滚将来者固自若也。亦犹论太极物物皆有之。而太极之体。未尝不存也。由是观之。则所谓太虚气之本体者。与太极为一。虽天地已辟。而太虚之本体自若。其可以此气谓往者过。来者续。而已往之气。已无所存乎。大抵天地未生之前。有所谓太虚者。包括太极之理。而为气之本体。太极之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乘此气而然也。朱子所谓动静者。所乘之机。指此而言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此气之动静而生天地也。故朱子曰。阴阳。形而下之器也。是故。以形而下之阴阳言之。则有始有终。虽天地之大。而亦有尽时。此则不可谓阴阳无始无终也。惟太虚之本体。不以先天地之既灭而亦灭。不以后天地之将生而亦生。一气长存。与理为体而元不相离。动而为天地万物之始。静而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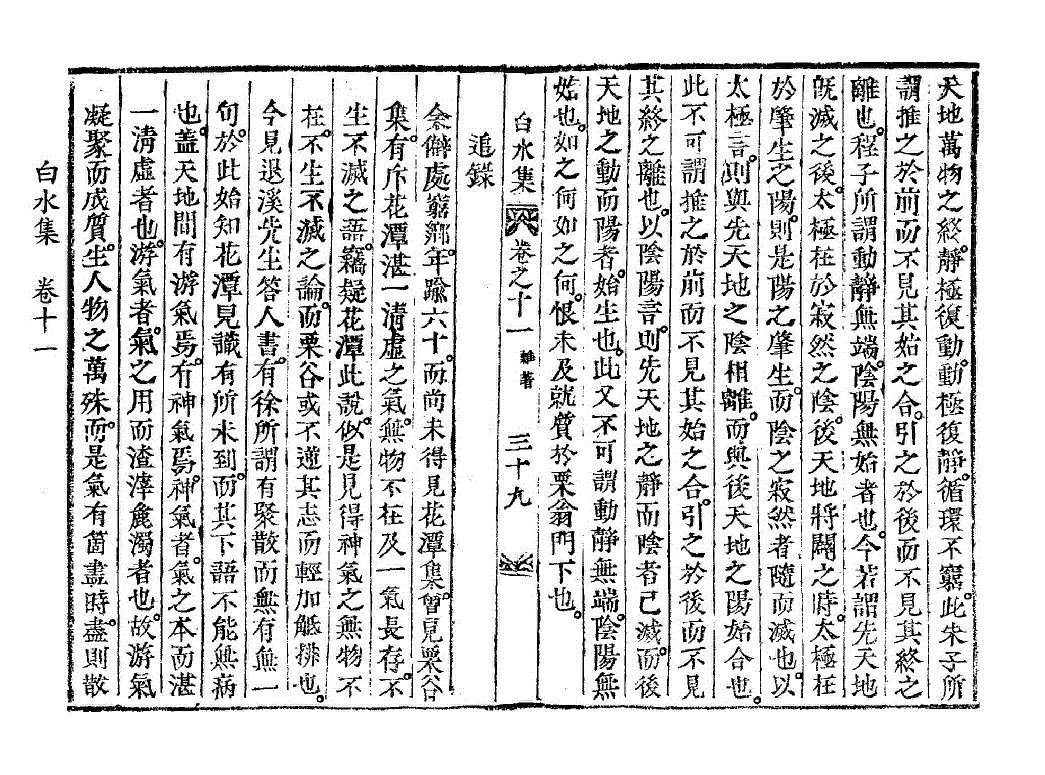 天地万物之终。静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不穷。此朱子所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也。今若谓先天地既灭之后。太极在于寂然之阴。后天地将辟之时。太极在于肇生之阳。则是阳之肇生。而阴之寂然者随而灭也。以太极言。则与先天地之阴相离。而与后天地之阳始合也。此不可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以阴阳言。则先天地之静而阴者已灭。而后天地之动而阳者。始生也。此又不可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也。如之何如之何。恨未及就质于栗翁门下也。
天地万物之终。静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不穷。此朱子所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也。今若谓先天地既灭之后。太极在于寂然之阴。后天地将辟之时。太极在于肇生之阳。则是阳之肇生。而阴之寂然者随而灭也。以太极言。则与先天地之阴相离。而与后天地之阳始合也。此不可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以阴阳言。则先天地之静而阴者已灭。而后天地之动而阳者。始生也。此又不可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也。如之何如之何。恨未及就质于栗翁门下也。追录
余僻处穷乡。年踰六十。而尚未得见花潭集。曾见栗谷集。有斥花潭湛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及一气长存。不生不灭之语。窃疑花潭此说。似是见得神气之无物不在。不生不灭之论。而栗谷或不逆其志而轻加抵排也。今见退溪先生答人书。有徐所谓有聚散而无有无一句。于此始知花潭见识有所未到。而其下语不能无病也。盖天地间有游气焉。有神气焉。神气者。气之本而湛一清虚者也。游气者。气之用而渣滓粗浊者也。故游气凝聚而成质。生人物之万殊。而是气有个尽时。尽则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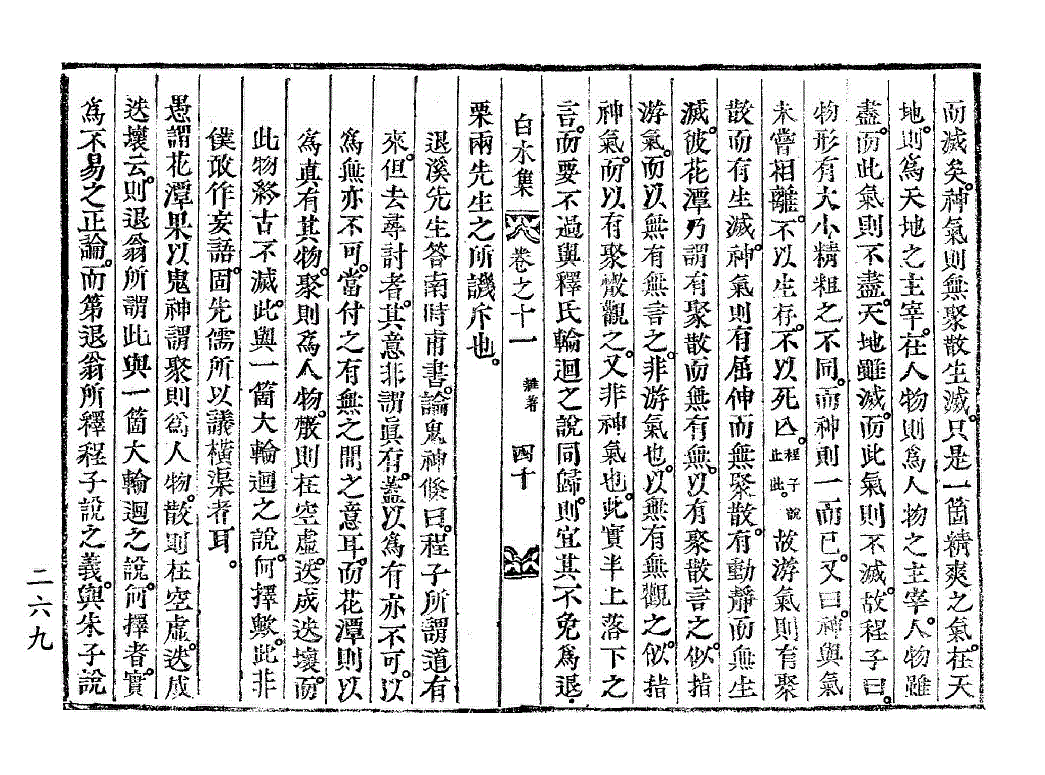 而灭矣。神气则无聚散生灭。只是一个精爽之气。在天地。则为天地之主宰。在人物则为人物之主宰。人物虽尽。而此气则不尽。天地虽灭。而此气则不灭。故程子曰。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而神则一而已。又曰。神与气未尝相离。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程子说止此。)故游气则有聚散而有生灭。神气则有屈伸而无聚散。有动静而无生灭。彼花潭乃谓有聚散而无有无。以有聚散言之。似指游气。而以无有无言之。非游气也。以无有无观之。似指神气。而以有聚散观之。又非神气也。此实半上落下之言。而要不过与释氏轮回之说同归。则宜其不免为退,栗两先生之所讥斥也。
而灭矣。神气则无聚散生灭。只是一个精爽之气。在天地。则为天地之主宰。在人物则为人物之主宰。人物虽尽。而此气则不尽。天地虽灭。而此气则不灭。故程子曰。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而神则一而已。又曰。神与气未尝相离。不以生存。不以死亡。(程子说止此。)故游气则有聚散而有生灭。神气则有屈伸而无聚散。有动静而无生灭。彼花潭乃谓有聚散而无有无。以有聚散言之。似指游气。而以无有无言之。非游气也。以无有无观之。似指神气。而以有聚散观之。又非神气也。此实半上落下之言。而要不过与释氏轮回之说同归。则宜其不免为退,栗两先生之所讥斥也。退溪先生答南时甫书。论鬼神条曰。程子所谓道有来。但去寻讨者。其意非谓真有。盖以为有亦不可。以为无亦不可。当付之有无之间之意耳。而花潭则以为真有其物。聚则为人物。散则在空虚。迭成迭坏。而此物终古不灭。此与一个大轮回之说。何择欤。此非仆敢作妄语。固先儒所以议横渠者耳。
愚谓花潭果以鬼神谓聚则为人物。散则在空虚。迭成迭坏云。则退翁所谓此与一个大轮回之说。何择者。实为不易之正论。而第退翁所释程子说之义。与朱子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第 2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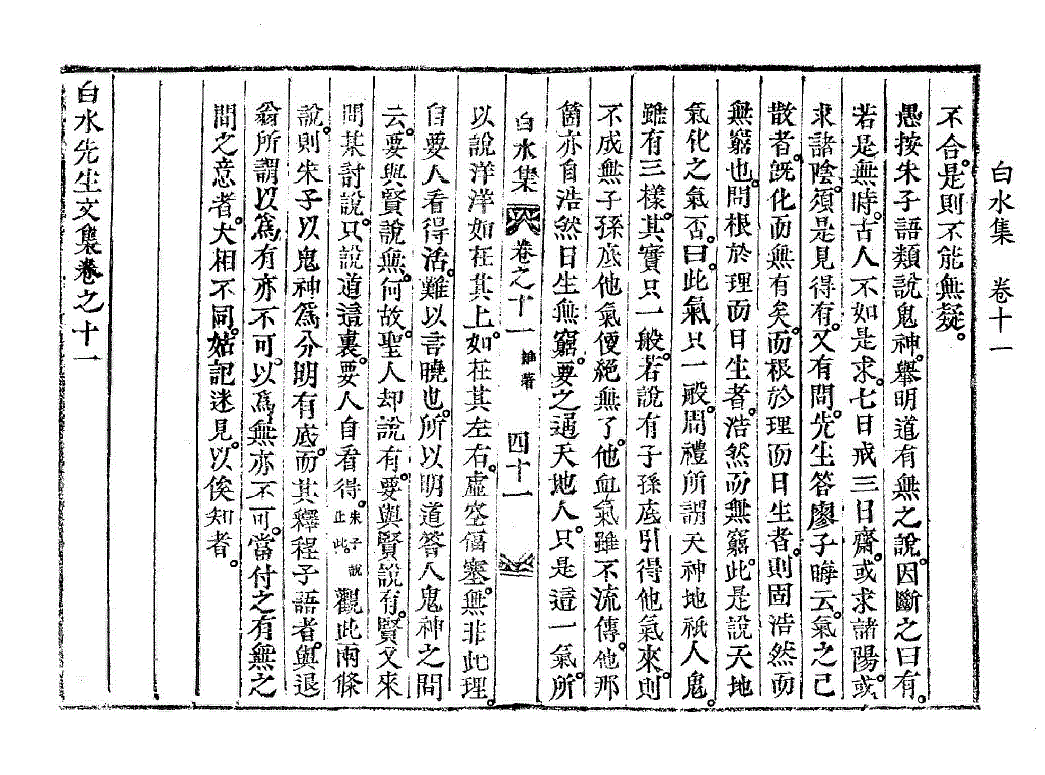 不合。是则不能无疑。
不合。是则不能无疑。愚按朱子语类说鬼神。举明道有无之说。因断之曰有。若是无时。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斋。或求诸阳。或求诸阴。须是见得有。又有问。先生答廖子晦云。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问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无穷。此是说天地气化之气否。曰。此气只一般。周礼所谓天神地祇人鬼。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自浩然日生无穷。要之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虚空偪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问云。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道这里。要人自看得。(朱子说止此。)观此两条说。则朱子以鬼神为分明有底。而其释程子语者。与退翁所谓以为有亦不可。以为无亦不可。当付之有无之间之意者。大相不同。姑记迷见。以俟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