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杂著
杂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7H 页
 师席禀目(附陶庵先生答)
师席禀目(附陶庵先生答)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为怪异之事。尧舜孔子只是庸。夷齐所为。都不是庸了。夷齐所为。何以谓之都不是庸也。如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谓之非庸。可也。如让国守节。何不得为庸。孔子既许夷齐以求仁得仁。仁而不庸者有之乎。朱子亦尝许伯夷以中立不倚。中立不倚而不庸者有之乎。圣贤之言。何若是矛盾也。难者曰。夷齐之事。仁则仁矣。中则中矣。然让国谏伐。皆非常之事。何可谓庸乎。此则不通之论也。朱子之言曰。尧舜禅授。汤武放伐。虽其事异常。然皆是合当如此。便只是常事。夷齐之让国谏伐。虽是非常之事。亦皆合当如此。则亦只是常事。何独不得为庸。愿下明教。
夷齐圣之清。固一节之士也。尧舜之禅授。汤武之放伐。虽其事异常。而便只是常事。苟于此看得透。则让国谏伐之都不是庸。可知也。
中庸首章小注云峰胡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字是统体一太极。率性之谓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极也。沙溪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两道字一也。胡氏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7L 页
 分而二之非是。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却继善成性而有先后之分矣。统体之太极。则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矣。○愚按沙溪之言。统体太极。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则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则恐不然。盖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物未生之前。太极之流行乎两仪者也。率性之谓道。人物已生之后。太极之流行于万物者也。理虽一也。所指则不同。恐不可直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也。如何。
分而二之非是。盖一阴一阳之谓道。对却继善成性而有先后之分矣。统体之太极。则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矣。○愚按沙溪之言。统体太极。不可与各具者。分先后则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则恐不然。盖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物未生之前。太极之流行乎两仪者也。率性之谓道。人物已生之后。太极之流行于万物者也。理虽一也。所指则不同。恐不可直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是率性之谓道也。如何。两道字。固一也。然一阴一阳。与率性之谓。地头略殊。云峰之说。恐不必深非。
造端乎夫妇。端字。应秀初知为君子行道之端。先生以道之端为教。不敢分解。退而思之。则终不能无疑。盖事有终始。道无终始。其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犹曰行仁自孝悌始也。若曰。道之端造乎夫妇。则是似以道为有终始也。如何。
道之端三字。语头甚重。恐失鄙人本意矣。苟曰行道之端。则于察乎天地一段。通乎否乎。试更思之。
孟子见梁襄王章。孰能与之能字。可疑。盖一之上。固合着能字。与之上。则未知其合着。
当时义理不明。但以战争为事。襄王于孟子。不嗜杀能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8H 页
 一之语。疑其迂而不足信。盖不知天下莫不与之义。则与字上着能字。又何疑乎。
一之语。疑其迂而不足信。盖不知天下莫不与之义。则与字上着能字。又何疑乎。觳觫章。天下之欲疾其君。欲字亦未详。
疾其君云云。语势有未安。一欲字岂宛转为辞而然耶。
丧服疏所论虽承重不得三年者有四种。而其一曰。传重非正体。庶孙为后。是也。此继祖若曾祖之嫡孙。为其庶孙为后者之服也。庶孙承重者。丧其长子。则其服当与此同耶异耶。见今应秀之族大父别检讳梦举之子大震。以继高祖之嫡孙。死而无后。故其弟大仪之子汉泰。为大震之后。此所谓庶孙承重者也。而今其长子鋈死。汉泰之服其子当如之何。昔年鄙族。又有如此之丧。赵处士世维议其服制。定以期年。则南原有一士人。深讥其非礼矣。今又有此丧。则当时讥赵之人。力主其所见。遂定以三年云。未知孰是孰非耶。愚意则欲从赵议。而不敢身质。敢此仰禀。
应秀与尹进士昌鼎。解得费隐之说不同。尹友则曰费字。朱子释之曰用之广也。隐字。朱子释之曰体之微也。则体用自有分别。静者为隐。动者为费。应秀则曰用之广。体之微。言虽殊。而实则一也。盖是道也。无物不具。无处不有。则是所谓费也。无物不具。无处不有者。非视听所及。则所谓隐也。费者即隐。而隐者即费也。不可分属动静。二说孰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8L 页
 为人后者。礼既同于众子。恐不得为其长子服斩也。如何如何。所论费隐之说。尹君不及左右。然左右之言。无亦伤快否。不可分属动静则明矣。
为人后者。礼既同于众子。恐不得为其长子服斩也。如何如何。所论费隐之说。尹君不及左右。然左右之言。无亦伤快否。不可分属动静则明矣。备要小祥条下注。引朱夫子答曾无疑书曰。在今练祥之礼。却当计月日实数为节。但其间忌日。却须别设祭奠。始尽人情耳。其间忌日别设祭奠之时祝文。何以为之耶。今有人遭其亲丧。临大祥之月。而病不能与祭。故于其忌日。不得已使其子设奠行祭。祥祭则待自家病间之日。追行为计。而其忌日祭祝文。请于应秀。应秀不敢对。而以书就禀焉。且其人又问退行之祥若在迩。则禫祭可行于应禫之月。而若过累月。则当依曾子次月之礼。愚意则以为若过二十七月而祥。则既有过时不祭之文。似当不复行禫。若当二十七月。则当从语类祥后便禫。当如王肃之说。而祥祭之后。即行禫祭矣。未知何如。
大祥退行时。方有祝。忌日则只是一献。略伸哀情而已。恐当无祝也。(忌日前一日。以主祭者病重。退行祥祭。而来日则略设伸哀之意。因上食为告辞。似委曲。)过期不禫。见于礼书矣。二十七月则行大祥后仍禫。来示诚然。过是月则不可行也。
五服沿革图。为人后者之妻。为夫本生父母大功。而本生父母。为子之为人后者之妻无服。凡服率皆报服。而此独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9H 页
 不然。何也。
不然。何也。凡服正统外。皆为之报。妇于夫之本生父母大功。则本生舅姑。似亦当如之矣。难之者曰。众子妇为大功。而出继子妇。又为大功。则恐非降等之义也。曰。众子是不杖期。而出继子亦不杖期。是亦非有降等也。出继之子。不得为正统。故必报之。子既如是。妇何独不然。家礼降服条。只云为人后者。为其私亲。皆降一等。私亲之为之也亦然。而五服逐条下。初不分属。沿革图之无所见。或与此一意耶。
三岁前。为他人所养育者。为养父母齐衰三年。见于家礼及备要。而三岁以后。则不复举论。若五六岁。或七八岁。孤哀无依。受养于他人者。为其养己者。当为何服。
幼时收养三岁以下与以上。难易悬绝。此制服之及于以下。而不及于以上者也。既无先王定制。则五六或七八岁被养者。只当斟量其恩义。自伸心制。而恐亦不敢为三年也。
问解。问祖丧未葬。又遭父丧。则当追服其祖三年否。沙溪引通解之说。以示服可再制之意。末云但亡在练后。则只伸心丧云者。未知恰当否也。此则引而不发之言也。今若有嫡子未终丧而亡嫡。孙承重者。其父之亡。在小祥后。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29L 页
 其受服变除之节。当如之何。
其受服变除之节。当如之何。此是疑礼大节目。以沙翁而犹持疑难决。则愚安敢妄有论断。然通典。只伸心丧之说。终有通不得处。父既亡矣。忍令祖丧仍无主祭之人耶。设令无明證。其当代为之服。恐是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者。故曾前有人以此来问者。则辄令于父丧成服之日。仍即为祖制服。成服在练后。亦如之矣。未敢知果如何也。盖闻尤庵定论如此。而未及见其明据矣。○后考尤庵礼疑。果有明据。玆以录示于下。○老先生尝以只伸心丧之说。为大不安。盖代父承重。是礼经之大节目。且祖丧练后。不可不祭。如祭则当服何服。故必如老先生之说。然后节节理顺矣。所谕父丧成服后。服祖服者。非鄙说。乃老先生之说也。且父丧成服之后。适值朔望。则可以服祖。若朔望相远。则其间祭祖时。当服何服。以此知服父服后。不待朔望。而即服祖服之说。为得也。
贤人为士林之所宗仰。至于建祠血食者。其子孙亲尽。无复可以奉祀者。则其神主当埋之耶。抑当为不迁之位。而百代奉祀耶。
文庙从祀之大贤。 太庙配食之功臣。皆当不迁。此外则皆僭也。于斯二者。俱无所当。为子孙者。安敢以私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0H 页
 而擅行耶。湖南此弊最多。恐不可不尽为釐正。然既无釐正之 朝令。则其子孙之贤者。只可自为之。而百拜告辞之前。又当先为具由以告矣。
而擅行耶。湖南此弊最多。恐不可不尽为釐正。然既无釐正之 朝令。则其子孙之贤者。只可自为之。而百拜告辞之前。又当先为具由以告矣。礼记玉藻。大夫带四寸。杂带。君朱绿。大夫玄华。士缁辟二寸。再缭四寸注。大夫以上带皆广四寸。士练带惟广二寸。而再缭腰一匝。则亦是四寸矣。备要深衣条再缭义。与此不同何。抑沙溪别有所考耶。
再缭一节。玉藻本意。则分明以二寸再缭于腰。而亦为四寸耳。要诀则以再缭为结两耳之法。此虽从家礼之文。而与玉藻不同矣。尤庵亦以此为疑。自谓恨未及先师在时奉质也。
家礼祭馔图鱼肉。沙溪以为非生鱼肉。乃鱼汤肉汤也。栗谷之用生。虽本于书仪。与仪礼馈食礼不同。参用生熟。虽是古礼。至于家礼。则朱子以燕器代祭器。常馔代俎肉。则不用生明矣。应秀曾信此语。不用生鱼肉矣。间尝窃究神理。则血祭甚有妙理。遂有疑于不用生之语。欲考仪礼而不得。近看礼记。其在郊特牲曰。腥剔爓腍祭。岂知神之所飨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此实不易之格言也。其在乐记曰。熟烹而祀。非达礼也。注熟烹牲体而荐。不如古者血腥之祭。为得礼意。故云非达礼也。以此观之。尤不可不用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0L 页
 也。又杂记曰。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又曰。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注。长乐陈氏曰。衅者涂衅以血。交神明之道也。观此数语。则腥血之有关于交神可知。栗谷之用生。实得礼意。从今决欲用生。而不敢自用。敢以仰质。
也。又杂记曰。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又曰。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注。长乐陈氏曰。衅者涂衅以血。交神明之道也。观此数语。则腥血之有关于交神可知。栗谷之用生。实得礼意。从今决欲用生。而不敢自用。敢以仰质。用生一节。实得古礼本意。来示甚好。然而尤庵先生以为家礼只说鱼肉则或生或熟。皆似无妨。但要诀俾用生鱼腥肉矣。家礼凡祭需皆熟。独于此用生腥。则恐非纯用家礼之意矣。近世士大夫往往用生腥一二器者。是则盖参取要诀备要而为之。惟在裁择之如何耳。
丧礼备要。门状祇慰某位。平交云某官。某位与某官何别。
某位。恐是如先生尊丈之称。至于称官。则视此稍下。然古人称号。有不可详。不敢质言。
妻之父称外舅。母称外姑。见于辑览中。某亲称号类。而妻之祖父母称号。则不见于其中。今有书于妻祖父母者。其称号当如何。
尤庵之答人问。以为于书札。则前面书上书某宅执事。若称之于他人。则依俗称丈祖无害也。
亲丧。兄弟在外。闻丧有先后。则先满者先除。后满者后除。故大全曰。练祥之礼。却当计月日实数为节。今若闻丧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1H 页
 于亲死之明日。则练祥除服。亦当不以其忌日而以其明日耶。
于亲死之明日。则练祥除服。亦当不以其忌日而以其明日耶。月日实数为节。固是朱子正论。而尤庵以为闻讣在亡月。则只计月数。而行练祥于亡日。此亦一道。然以孝子之心言之。只当从朱子说。
伯父之称之义云何。
伯父云者。谓诸父之中。不论伯仲叔季。称生父当为伯父。曾见古人如此说。而今考不得。故不敢终守其说。尤庵则以为当从父之次第。称伯或称仲叔季云矣。
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按周礼地官司徒下篇。载师掌任土之法注。所谓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者。盖言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者也。若不在官之工商。尽以此例受田。则无乃太过乎。
士工商之受田者。则必知其在官。来示似然。
去年讲诗时。关雎寤寐反侧之忧。琴瑟钟鼓之乐。先生以为宫人之忧乐。弟子悦服矣。退而读论语。至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章。详见其小注朱子曰。此诗看来。是宫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侧。外人做不到。诗本篇小注亦然。以此观之。则其所谓寤寐反侧。为文王事无疑矣。敢问前日之教。何所据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1L 页
 关雎集注。则分明以寤寐反侧。琴瑟钟鼓。属之宫人。朱子之说。固或有不同者。而只当以集注为正也。或云小注所载说。亦不必断以为文王事也。
关雎集注。则分明以寤寐反侧。琴瑟钟鼓。属之宫人。朱子之说。固或有不同者。而只当以集注为正也。或云小注所载说。亦不必断以为文王事也。鲁之禘。孔子谓之非礼。若使鲁之后君。有如周公者作。则其处之当如何。盖不王而禘。虽是僭礼。天子既赐之矣。始封之君。既受之矣。而世世遵行之。则一朝废之。亦甚未安。如之何则可也。
鲁之禘。受与赐成王伯禽。当分其责。若使后世。有文王周公者作。则其变而归正也。必有道矣。下于此者。则恐不能也。
问解续。池宁海问上年十二月。改葬父母。以新占山运拘忌。即为权厝。永窆之期。卜在冬间。谓葬事未毕仍服。欲经来冬。永窆而除之。未除之前。或有倘来所难避者。去就狼狈。慎独斋答曰云云。○愚按阴阳拘忌。礼经所无。则拘于山运。破墓经年而不葬。失礼之甚者。为此失礼之甚者。议其制服。恐非扶世教。尊圣法之君子所屑为也。假使有议。亦未知其必如是也。夫浅土权厝。与山殡无异也。以此而谓为襄奉。晏然除服于三月之后。而从仕宴乐。与他人无异。则是岂孝子恻怛之诚心哉。人子事亲之道。恐不可若是草草也。为父母服丧。止于三年。而未葬则虽过三年。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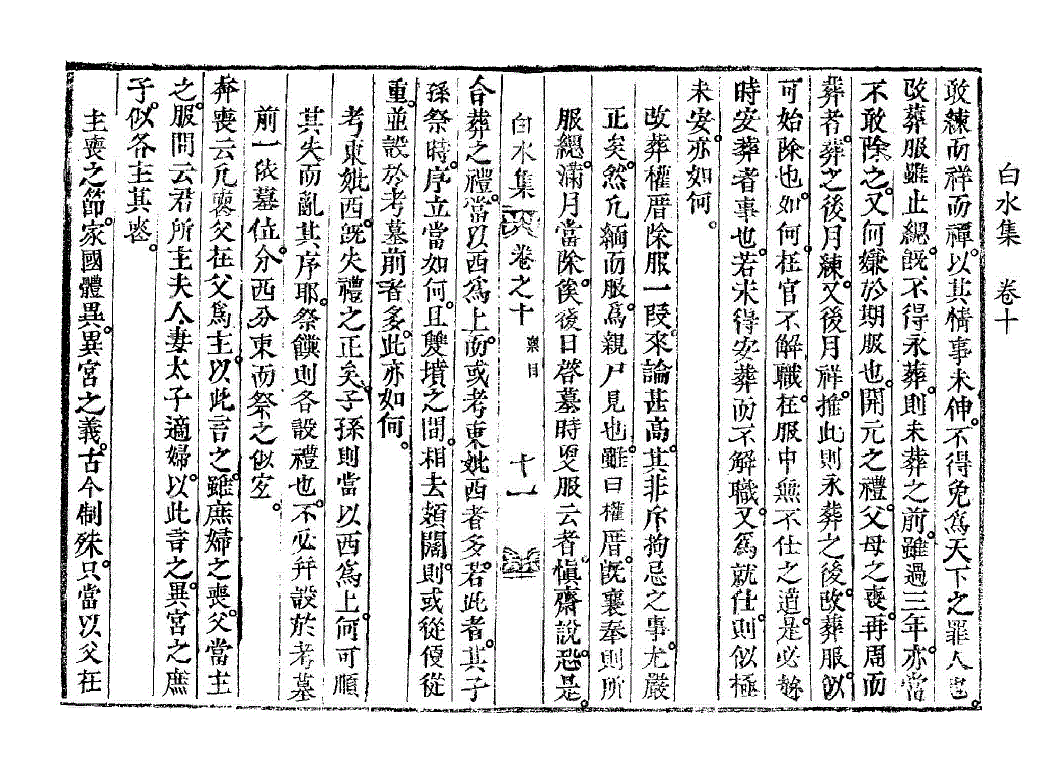 敢练而祥而禫。以其情事未伸。不得免为天下之罪人也。改葬服虽止缌。既不得永葬。则未葬之前。虽过三年。亦当不敢除之。又何嫌于期服也。开元之礼。父母之丧。再周而葬者。葬之后月练。又后月祥。推此则永葬之后。改葬服。似可始除也。如何。在官不解职。在服中无不仕之道。是必趁时安葬者事也。若未得安葬而不解职。又为就仕。则似极未安。亦如何。
敢练而祥而禫。以其情事未伸。不得免为天下之罪人也。改葬服虽止缌。既不得永葬。则未葬之前。虽过三年。亦当不敢除之。又何嫌于期服也。开元之礼。父母之丧。再周而葬者。葬之后月练。又后月祥。推此则永葬之后。改葬服。似可始除也。如何。在官不解职。在服中无不仕之道。是必趁时安葬者事也。若未得安葬而不解职。又为就仕。则似极未安。亦如何。改葬权厝除服一段。来论甚高。其非斥拘忌之事。尤严正矣。然凡缅而服。为亲尸见也。虽曰权厝。既襄奉则所服缌。满月当除。俟后日启墓时更服云者。慎斋说。恐是。
合葬之礼。当以西为上。而或考东妣西者多。若此者。其子孙祭时。序立当如何。且双坟之间。相去颇阔。则或从便从重。并设于考墓前者多。此亦如何。
考东妣西。既失礼之正矣。子孙则当以西为上。何可顺其失而乱其序耶。祭馔则各设礼也。不必并设于考墓前一依墓位。分西分东而祭之似宜。
奔丧云凡丧父在父为主。以此言之。虽庶妇之丧。父当主之。服问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适妇。以此言之。异宫之庶子。似各主其丧。
主丧之节。家国体异。异宫之义。古今制殊。只当以父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2L 页
 父为主为经也。
父为主为经也。权华山𪼛之殁也。戒其门人曰。他日南人中。必有为张氏。请复位疏者。若参其疏。则不免为千万古小人。汝曹识之。赵处士世维闻之。击节叹赏。而其哭华山诗曰。临终一语扶伦志。正使千秋大义明。其后辛壬间。南人果上疏。而承华山之训者不与焉。近者安丈璛述华山言行而删此一节。问其故。则以为小事不必记。且恐华山之以此见恶于南人故阙之也。应秀累为之言。而终不见听。此果何如。
临终一语。实为扶伦之义。处士既无事业之见于世。则于此犹可验其学识之出常。记其言行者。乌可去此一端。若怕人见恶而故去之。则恐非有识者所为。安公岂为是哉。未敢信也。
嫡子废疾。嫡孙代服。有朱子定论。似无可疑。但恐不可自为传重正主。其旁题及祝文。以其父名为之。而嫡孙服斩。摄行馈奠。何如。
废疾者。使嫡子代服。既有朱子定论。更无可疑。但乙卯后尤庵为群凶所构诬。而此事又其一端。玄石亦坐此削版。自此以后。为世所忌讳。鲜有行之者。然当此变故者。果能的知礼意之不可容已。凶论之不足挠夺。则谁禁而莫之为乎。只当说与此道理。令其人量处而已。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3H 页
 于题主。玄石主此论。而尤庵是之矣。然未知其时。闵家果行得否也。
于题主。玄石主此论。而尤庵是之矣。然未知其时。闵家果行得否也。夷齐之逃。当在何时。父死未殡而逃去。则人情之所不忍也。若既殡而后逃去。则殡前谁为丧主。
夷齐逃去。若在既殡之后。则殡前主丧之节。诚若难处。然古时丧礼颇未备。不若后世之详密。况此事重在让国。馀外细节。不必起疑。
讲粹语心说
退溪先生曰。湛一。气之本。当此时。未可谓之恶。然气何能纯善。惟是气未用时。理为主。故纯善耳。
愚按湛一者。清明纯一之谓也。既曰湛一。则何尝不纯善乎。惟其所谓用事之气。乃是粗底血气。而非湛一之本体也。此心未发之前。血气静寂。与湛一无间。故此时则纯善无恶。及其情动。然后血气用事。而善恶分焉。退翁之言。则以湛一之气。为未能纯善。而谓未发之前。理为主则纯善。已发之后。气用事则为恶。若然则是气也。乃是含两头者。何可谓之湛一也。恨未及就正于退翁门下也。
朴签曰。气何能纯善。气未用事。两气字。只是泛言气。下气字。亦不必专属粗底血气。如是看则退溪说。恐不为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3L 页
 俞签曰。此段杨兄所论似然矣。而朴兄则以为不为病。大抵于论气处。彼此意见。本不相合。则于此段。无怪其若此。
俞签曰。此段杨兄所论似然矣。而朴兄则以为不为病。大抵于论气处。彼此意见。本不相合。则于此段。无怪其若此。七情之发。虽不可谓不由于五性。然与四端之发。对举而言。则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故端易微而情已暴。其势然也。
愚按退溪说。极为精微。然四端只是七情中善一边。而非七情外别有之情也。则四七恐未可判作两物。而分属理气也。愚则以为四端七情。莫不本于五性。而四端。心之神明。纯乎本然而发者也。七情。杂乎血气而发者也。故端则纯善无恶。情则有善有恶。未知如何。
朴签曰。四七之说。栗谷所辨。无容更议。然主于理主于气之云。亦与理发气发之说。有间。未可直以判作两物为言也。
俞签曰。此段杨兄所论。愚则以为以下甚好。
栗谷先生曰。夫理之本然。则纯善而已。乘气之际。参差不齐。清净至贵之物及污秽至贱之处。理无不在。而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若以污贱谓非理之本然则可。遂以为污贱之物无理则不可也。
愚按理之本然。纯善而已。乘气之际。参差不齐云者。其语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4H 页
 意有若以为理之本然。悬空独立之时则纯善而已。及至乘气之际。始有参差不齐者然。然则理气未免有离合之时。其与元不相离之说。岂不相悖乎。且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一段。亦恐未安。盖清净污秽有贵贱之异者气也。精粗本末。无彼此之殊者理也。若在清净理亦清净。在污秽理亦污秽。则是理有彼此之殊也。其可谓阴阳一太极乎。
意有若以为理之本然。悬空独立之时则纯善而已。及至乘气之际。始有参差不齐者然。然则理气未免有离合之时。其与元不相离之说。岂不相悖乎。且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一段。亦恐未安。盖清净污秽有贵贱之异者气也。精粗本末。无彼此之殊者理也。若在清净理亦清净。在污秽理亦污秽。则是理有彼此之殊也。其可谓阴阳一太极乎。朴签曰。栗谷此段。盖言理之本然则纯善。而其所以异者由气也。不可以有离合疑之。理亦清净。理亦污贱者。亦言其气质之性。而性之本然。又未尝不在其中。则岂不可谓阴阳一太极乎。
俞签曰。此段。朴兄之言好。
尤庵先生曰。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释。殊不甚安。故尝以为当以形字为主。而处道字器字于形之上下。以形道器为三件物事。则所释井井。无难见矣。二先生则以形与道为二。而以形与器为一。似与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故中庸首章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语类亦曰。形而上。全是天理。形而下。只是那渣滓。至于形。又是渣滓至浊者。是皆以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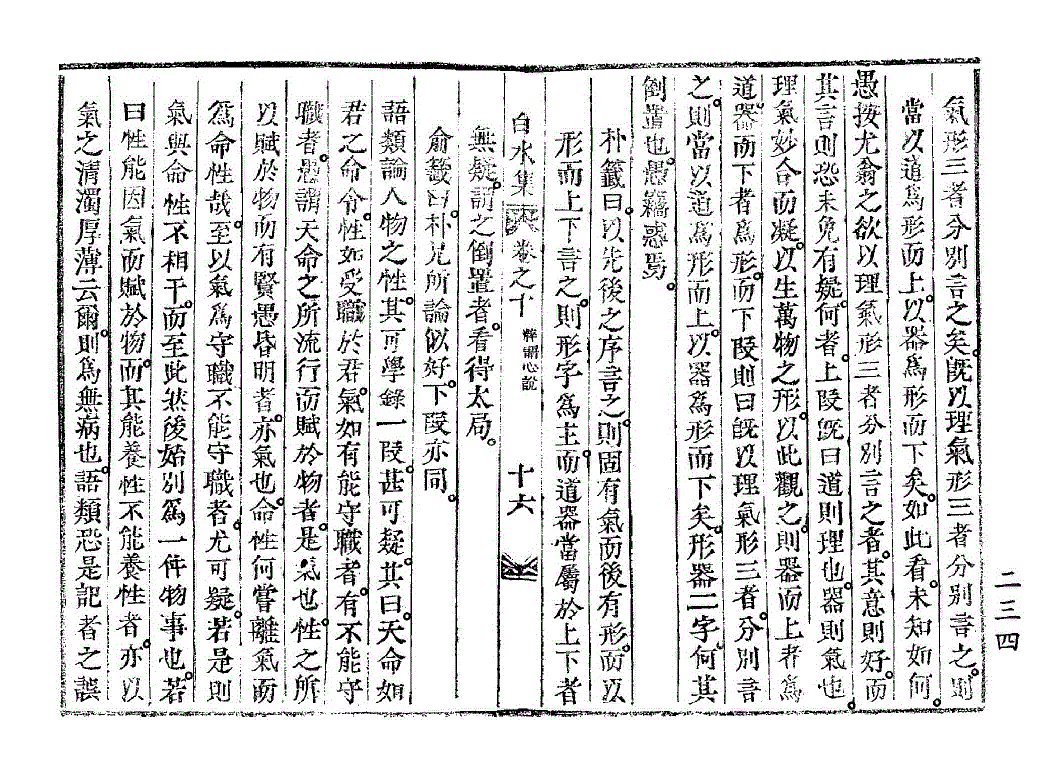 气形三者分别言之矣。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而上。以器为形而下矣。如此看。未知如何。
气形三者分别言之矣。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而上。以器为形而下矣。如此看。未知如何。愚按尤翁之欲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者。其意则好。而其言则恐未免有疑。何者。上段既曰道则理也。器则气也。理气妙合而凝。以生万物之形。以此观之。则器而上者为道。器而下者为形。而下段则曰既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而上。以器为形而下矣。形器二字。何其倒置也。愚窃惑焉。
朴签曰。以先后之序言之。则固有气而后有形。而以形而上下言之。则形字为主。而道器当属于上下者无疑。谓之倒置者。看得太局。
俞签曰。朴兄所论似好。下段亦同。
语类论人物之性。其可学录一段。甚可疑。其曰。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职于君。气如有能守职者。有不能守职者。愚谓天命之所流行而赋于物者。是气也。性之所以赋于物而有贤愚昏明者。亦气也。命性何尝离气而为命性哉。至以气为守职不能守职者。尤可疑。若是则气与命性不相干。而至此然后始别为一件物事也。若曰性能因气而赋于物。而其能养性不能养性者。亦以气之清浊厚薄云尔。则为无病也。语类恐是记者之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5H 页
 也。
也。愚按语类说极好。其曰天命如君之命令者。所以明天所赋为命也。其曰性如受职于君者。所以明物所受为性也。天以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人物。而赋之以当然之理。则是犹命令。而命未尝离乎气也。人物禀阴阳五行之气。以为人物。而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性。是犹受职而性未尝离乎气也。尤翁何以疑其离气而为性命也。愚则未见其离气也。但语类受职于君四字。改以所受于君之职。则似尤为恰好也。至于尤翁所谓以气为守职不能守职。尤可疑者。愚则尤窃惑焉。夫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惟人心最灵。不失其性之全。而物则不能。君子修之而小人悖之。此非气之有能守职有不能守职者乎。尤翁之以语类疑为记者之误者。恐不然。而至其所自为说。则曰性能因气而赋于物。性岂有能之物乎。此恐为语病。且其所谓始别为一件物事之别字。其义未可详也。
朴签曰。语类此段。以命性气三者各言之。气字别言于命性之后。则气自为一件物事。而命性似离气为命性。尤翁所疑。似以此矣。
问。五性是五行之理。五行属于五脏。则宜乎五脏各统一性。而今以五性皆统乎心者何邪。曰。天下万物。无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5L 页
 配属于五行者。谓五行之理赋于人而为五性则可也。因以为凡配五行者。皆有仁义礼智之性。则大不可。凡配五行者。或以形。或以气。或以味。或以臭。今味之甘者。皆属于土。遂以蜜。为具信之性。可乎。
配属于五行者。谓五行之理赋于人而为五性则可也。因以为凡配五行者。皆有仁义礼智之性。则大不可。凡配五行者。或以形。或以气。或以味。或以臭。今味之甘者。皆属于土。遂以蜜。为具信之性。可乎。愚按人禀五行之气以生。故五行之理乘气而赋于人。若无是气。则理何能独赋于人乎。惟其有五脏之气。所以有五性之理。但五脏中四者。其体实。故其理无以著。惟心则其体虚。故五脏之精气。聚于方寸之中。而五性以著。若曰心独有五行之理。而肾肝脾肺。只有气而无是理。则岂不为未安乎。且味之甘者。皆属土。故五味之中。惟甘独能调和五味。此是信之理也。则谓蜜不具信之理者。亦未知其必然也。
朴签曰。尤庵此条。固不无可疑。更详之。
俞签曰。杨兄所论极好。愚亦平日所尝致疑者矣。
讲粹语心说[再]
湛一气之本然。气何能纯善云云。朴兄不以为病之无怪。诚如高明之签教。今不须多辨。第审高明签教似然二字。恐亦非快许之意。请与高明更商可乎。愚按朱子之言曰。心字一言而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其心必仁。仁则生矣。若使心气果不能纯善。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6H 页
 则朱子何以有此必仁之训乎。朱子又曰。四端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是此性之理所在也。由是观之。则四端之发。莫非此心之气也。惟其气之纯善也。故其发见之端。若是纯善。是气也。安得不谓之纯善乎。大抵湛一者。神气也。用事而有善有恶者。血气也。而退溪先生理发气随等说。盖以神气专属理。故其论气字。则专主血气。而有此何能纯善之语。此与陈安卿气含两头之言。前后一揆。而其与湛一气本之言。未免矛盾。如何。
则朱子何以有此必仁之训乎。朱子又曰。四端是心之发见处。四者之萌。皆出于心。而其所以然者。是此性之理所在也。由是观之。则四端之发。莫非此心之气也。惟其气之纯善也。故其发见之端。若是纯善。是气也。安得不谓之纯善乎。大抵湛一者。神气也。用事而有善有恶者。血气也。而退溪先生理发气随等说。盖以神气专属理。故其论气字。则专主血气。而有此何能纯善之语。此与陈安卿气含两头之言。前后一揆。而其与湛一气本之言。未免矛盾。如何。朴签曰。杨友既弃鄙说。更与高明商确。固不当容喙于其间。然既蒙俯询。安可徒默。若以二气。各立为二物。而议前贤之说。则恐无处不为可疑之端。未知高见竟以为何如也。
俞签曰。四端之发。莫非此心之气以下。止血气也。所论诚好矣。而惟退溪先生理发气随等说。盖以神气专属理云云。未知退溪本意。果如此。
主于理。主于气之云。与理发气发之说。有间云者。朴兄之言然矣。然以四端专属主理一边。以七情专属主气一边。此非判作两物而何。愚于此。又生一疑焉。主于理而气随之。则不成说话。若曰心主于理而气随之。则是其气似为心外之气也。此恐未稳。愚意此句若改之曰。理为主而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6L 页
 随之。则似为无病。未知如何。
随之。则似为无病。未知如何。俞签曰。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一段。栗翁之意。盖以为四端之发。虽纯乎义理。而其发之者。即气也。故曰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之发。虽杂乎血气。而其所以发者。即理也。故曰。主于气而理乘之。此不过谓四端七情。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之意也。然若就气上论之。则四端七情。莫不本于五性。而四端心之神明。纯乎本然而发者也。七情心之神明。杂乎血气而发者也。夫本然之气(即心之本体)纯善。故端亦纯善。血气之气(即血气精英)有善恶。故情亦有善恶。如此看得。不知其为病。如何。
朴签曰。此亦以二气为二物。故于不当疑处。转生葛藤。
理之本然。纯善而已。乘气之际。参差不齐云云。栗翁本意。岂以理气有离合之时。而其语势则恐易致人疑。故愚敢有所云云。而朴兄签教云。此段盖言理之本然。则纯善。而其所以异者。由气也。不可以有离合疑之。此则可以破后人之惑也。但其所谓理亦清净。理亦污浊者。亦言其气质之性。而性之本然。又未尝不在其中云云一段。则恐未足以破惑。何者。理之本然则纯善。而气质之清浊粹驳有万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7H 页
 不齐。故在清净则理无所拘蔽。而全体呈露。在浊驳则理为浊驳之所拘蔽。而不得呈露。然其本体之纯善。则自如也。此之谓性之本体。未尝不在其中者也。若如栗谷之言。在污贱理亦污贱。则是理之本体。随其气质而变矣。本体既变。则谓性之本然。未尝不在其中者。可乎。
不齐。故在清净则理无所拘蔽。而全体呈露。在浊驳则理为浊驳之所拘蔽。而不得呈露。然其本体之纯善。则自如也。此之谓性之本体。未尝不在其中者也。若如栗谷之言。在污贱理亦污贱。则是理之本体。随其气质而变矣。本体既变。则谓性之本然。未尝不在其中者。可乎。俞签曰。理之本然(止)不在其中者也一段。杨丈之言极好矣。朴兄所论。以有污贱之理。故有污贱之物云者。恐似有病。夫理者。本自清净。复岂有污贱之理乎。其为污贱者。即气也。而理在其中。但为污贱所拘。不得呈露。然其本体。则自如矣。栗翁所谓理亦清净。理亦污贱之亦字。承上在清净在污贱之在字而言。此亦字。不过理亦在其中之意。若观上理无不在一句。则可知。然则亦字。不必局看。
朴签曰。理亦污贱者。盖以有污贱之理。故有污贱之物。物既污贱。则其理亦自污贱。非谓本然之体污贱也。
形而上。形而下。孔子因论易与乾坤而言。此以明其道器之分。故本义释之曰。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此其意分明。以形与道为二。形与器为一也。而尤翁乃以形道器。为三件物事。以道处于形而上。以器处于形而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7L 页
 其违孔子本旨远矣。但朱子亦尝有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于阴之训。此则为一义也。尤翁之论。亦作一义看。则似为无妨。而其言形器之别。亦不甚明快。故愚于前日。不举其大可疑者。姑举其微疑处以质。而意谓高明穷格之论。必并及于其大可疑处。今承签教。则乃只以愚之所疑为不当疑。如此看书。恐无长进之理。殊可为欠。
其违孔子本旨远矣。但朱子亦尝有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于阴之训。此则为一义也。尤翁之论。亦作一义看。则似为无妨。而其言形器之别。亦不甚明快。故愚于前日。不举其大可疑者。姑举其微疑处以质。而意谓高明穷格之论。必并及于其大可疑处。今承签教。则乃只以愚之所疑为不当疑。如此看书。恐无长进之理。殊可为欠。朴签曰。形字看作形质。道字看作理。器字看作气。则谓之三件物事者。未见其为大病也。虽以卦爻阴阳言之。有可以形言者。有可以气言者。何可硬定为一物邪。
俞签曰。尤庵说何必作一义看。虽以杨丈所论本义说言之。卦爻阴阳。有气焉有形焉。形质即形也。而其理道也。其气器也。然则何以谓之不可为三件乎。
讲粹语心说[三]
湛一。气之本然云云条。得蒙许可。深以为幸。第退溪先生理发气随等语。盖以神气专属理云云一段。高明以为未知退溪本意果如此。退溪本意之所以不如此者。可得闻明教邪。此亦不可不一番商确者也。四端。主于理而气随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8H 页
 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一段。是退溪之言也。高明认以栗谷语。而以栗谷之意解说如此。由是观之。则退,栗两先生所见。初无不同。为之奉呵。盛签自若就气上论之。以下则好矣。但血气之气下注。以即血气精英。而其下继之曰。有善恶。故情亦有善恶。此恐未稳。盖精英根于血气。故虽或有不齐。然当其未发而粗底血气不及用事之前。此亦未尝不善。而南塘乃谓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此南塘所以不识心体也。今若曰精英有善恶云。则其不近于南塘之言乎。愚意此段改之曰。本然之气。至公无私。故端无有不善。血气之气。未能无私。故情或有不善云云似胜。未知如何。朴兄签纸。高明无所可否。何也。退翁所谓主于理而气随之云者。恐未为以理为气主之语。似不若改作。理为主而气随之。为分晓也。故愚之前签。有所云云。是盖只论理气而已。而朴兄签教乃云。此亦以二气为二物。故于不当疑处。转生葛藤。此则初不思省人意。只以一向非斥为主。而自不觉其言之鹘突也。如此讲论。恐不如不为之为无事也。
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一段。是退溪之言也。高明认以栗谷语。而以栗谷之意解说如此。由是观之。则退,栗两先生所见。初无不同。为之奉呵。盛签自若就气上论之。以下则好矣。但血气之气下注。以即血气精英。而其下继之曰。有善恶。故情亦有善恶。此恐未稳。盖精英根于血气。故虽或有不齐。然当其未发而粗底血气不及用事之前。此亦未尝不善。而南塘乃谓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此南塘所以不识心体也。今若曰精英有善恶云。则其不近于南塘之言乎。愚意此段改之曰。本然之气。至公无私。故端无有不善。血气之气。未能无私。故情或有不善云云似胜。未知如何。朴兄签纸。高明无所可否。何也。退翁所谓主于理而气随之云者。恐未为以理为气主之语。似不若改作。理为主而气随之。为分晓也。故愚之前签。有所云云。是盖只论理气而已。而朴兄签教乃云。此亦以二气为二物。故于不当疑处。转生葛藤。此则初不思省人意。只以一向非斥为主。而自不觉其言之鹘突也。如此讲论。恐不如不为之为无事也。栗谷说。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之亦字。高明以为不必局看。此其意虽好。然其本文文势。则似不如此。盖其本文所释。理有善恶一句。已自不同于朱子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8L 页
 说。而所谓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者。观其上下文义。分明以理为有不同。此岂或先生初年未到之见否。谨按圣学辑要。论心性情条按说曰。人虽至恶者。未发之时。固无不善。才发有善恶。其恶者。由于气。禀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体也。故曰。性则全善。以此推之。则栗翁之意。可知也。夫人之至恶者。即禀得气之污贱者也。而其性之本体。犹谓之全善。则此与所谓在污贱则理亦污贱者。岂不相反乎。于此。可见栗翁所谓乘气之际。参差不齐者。只谓理随气禀之不同。有或开或蔽或通或塞之异而已。非谓理之本体。随气变易而或善或恶也。彼南塘一派。不识栗翁本意之如此。而错认此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两句语。遂分别一原上本然与异体上本然。而以浑然纯粹之一太极。碎作千片万段。或全或偏。或巨或细。或善或恶之物。看书卤莽。察理不精之弊。乃至于斯。可不惧哉。此愚之所以不顾僭妄。必欲穷究极辨于此等义理。以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朋友间能知此心。而相与酬酢者鲜。良可叹惜。
说。而所谓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者。观其上下文义。分明以理为有不同。此岂或先生初年未到之见否。谨按圣学辑要。论心性情条按说曰。人虽至恶者。未发之时。固无不善。才发有善恶。其恶者。由于气。禀物欲之拘蔽。而非其性之本体也。故曰。性则全善。以此推之。则栗翁之意。可知也。夫人之至恶者。即禀得气之污贱者也。而其性之本体。犹谓之全善。则此与所谓在污贱则理亦污贱者。岂不相反乎。于此。可见栗翁所谓乘气之际。参差不齐者。只谓理随气禀之不同。有或开或蔽或通或塞之异而已。非谓理之本体。随气变易而或善或恶也。彼南塘一派。不识栗翁本意之如此。而错认此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两句语。遂分别一原上本然与异体上本然。而以浑然纯粹之一太极。碎作千片万段。或全或偏。或巨或细。或善或恶之物。看书卤莽。察理不精之弊。乃至于斯。可不惧哉。此愚之所以不顾僭妄。必欲穷究极辨于此等义理。以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朋友间能知此心。而相与酬酢者鲜。良可叹惜。形而上。形而下云云。高明与朴兄签教。并违于鄙见。而朱子之意。则终不如此。至于此等处。从众之道。有未可行者。玆敢复陈愚见如左。谨按朱子之言曰。形而上。形而下。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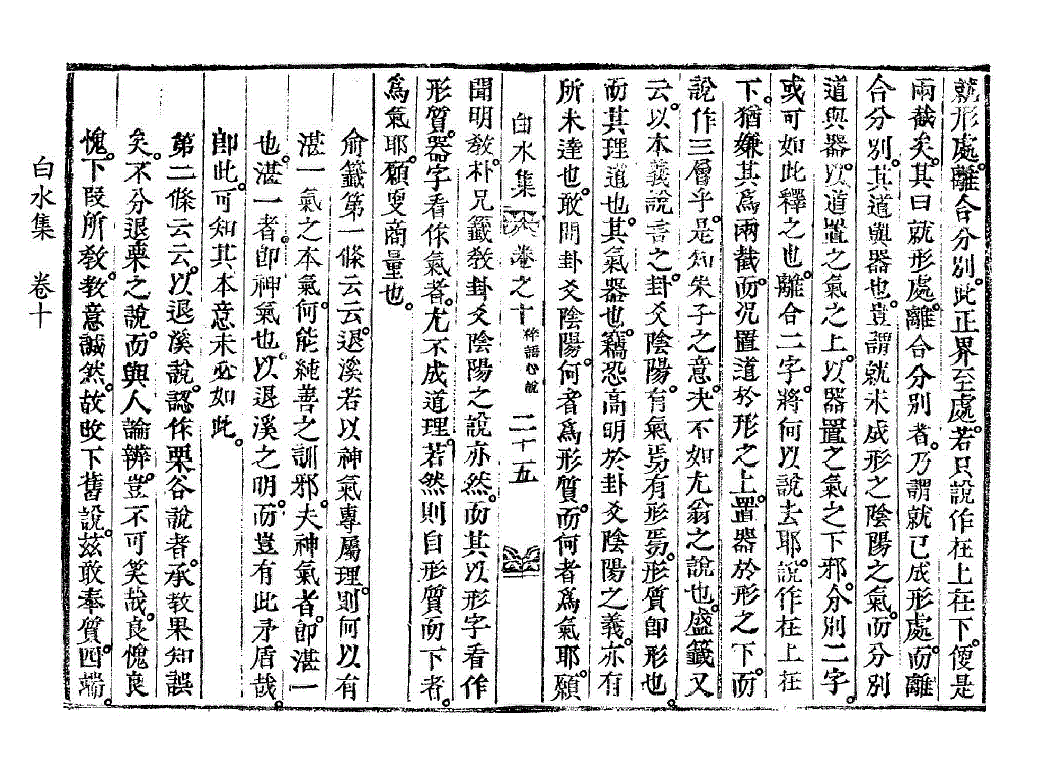 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界至处。若只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矣。其曰就形处。离合分别者。乃谓就已成形处。而离合分别。其道与器也。岂谓就未成形之阴阳之气。而分别道与器。以道置之气之上。以器置之气之下邪。分别二字。或可如此释之也。离合二字。将何以说去耶。说作在上在下。犹嫌其为两截。而况置道于形之上。置器于形之下。而说作三层乎。是知朱子之意。决不如尤翁之说也。盛签又云。以本义说言之。卦爻阴阳。有气焉有形焉。形质即形也。而其理道也。其气器也。窃恐高明于卦爻阴阳之义。亦有所未达也。敢问卦爻阴阳。何者为形质。而何者为气耶。愿闻明教。朴兄签教卦爻阴阳之说亦然。而其以形字看作形质。器字看作气者。尤不成道理。若然则自形质而下者。为气耶。愿更商量也。
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界至处。若只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矣。其曰就形处。离合分别者。乃谓就已成形处。而离合分别。其道与器也。岂谓就未成形之阴阳之气。而分别道与器。以道置之气之上。以器置之气之下邪。分别二字。或可如此释之也。离合二字。将何以说去耶。说作在上在下。犹嫌其为两截。而况置道于形之上。置器于形之下。而说作三层乎。是知朱子之意。决不如尤翁之说也。盛签又云。以本义说言之。卦爻阴阳。有气焉有形焉。形质即形也。而其理道也。其气器也。窃恐高明于卦爻阴阳之义。亦有所未达也。敢问卦爻阴阳。何者为形质。而何者为气耶。愿闻明教。朴兄签教卦爻阴阳之说亦然。而其以形字看作形质。器字看作气者。尤不成道理。若然则自形质而下者。为气耶。愿更商量也。俞签第一条云云。退溪若以神气专属理。则何以有湛一气之本气。何能纯善之训邪。夫神气者。即湛一也。湛一者。即神气也。以退溪之明。而岂有此矛盾哉。即此。可知其本意未必如此。
第二条云云。以退溪说。认作栗谷说者。承教果知误矣。不分退,栗之说。而与人论辨。岂不可笑哉。良愧良愧。下段所教。教意诚然。故改下旧说。玆敢奉质。四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39L 页
 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一段。退溪之意。盖以为四端之发。纯乎义理。故曰主于理。七情之发。杂乎血气。故曰主于气。然其发之者。皆是气也。若只就气上论之。则四端七情。虽本于五性。而四端。心之神明。纯乎本然而发者也。七情。心之神明。杂乎血气而发者也。夫本然之气。(即心之本体)至公无私。故端无有不善。血气之气。(即血气精英)未能无私。故情或有不善。如此看得。不至为病否。
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一段。退溪之意。盖以为四端之发。纯乎义理。故曰主于理。七情之发。杂乎血气。故曰主于气。然其发之者。皆是气也。若只就气上论之。则四端七情。虽本于五性。而四端。心之神明。纯乎本然而发者也。七情。心之神明。杂乎血气而发者也。夫本然之气。(即心之本体)至公无私。故端无有不善。血气之气。(即血气精英)未能无私。故情或有不善。如此看得。不至为病否。主于理而气随之一句。若改之以理为主。而气随之则其义固为分明。而主于理云者。亦似是理为主之意。如云四端之发。纯乎义理而已。如此等处。不以辞害义可矣。
第三条云云。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云者。盖谓理随气禀之不同。有或开或闭或通或塞之异。而非谓理之本体。随气变易而有善恶也。程子所谓人生气禀。理有善恶之训。亦以开闭通塞言之。而栗谷所释之义。不过如斯而已。然则愚之所自解者。或不至大悖否。
第四条云云。朱子所谓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界至处。若只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0H 页
 矣一说。正亦愚辈之所取而为据者也。愚何尝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分别道与气耶。既曰阴阳。则其已成形可知。虽以五行言之。五行之质。即形也。五行之气。即气也。至于卦爻亦然。何可谓之无形气之别耶。本义所论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夫形固是气之重浊者。则形亦同是气也。故朱子以形与气同谓之器。而若分而言之。则尤当如尤翁之说。然此非两截也。又非三层也。就已成形处。分别其道与器而已。离而言之。曰道曰器。合而言之。道亦器。器亦道。然则离合二字。亦何谓之说不得邪。朱子所谓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云者。其病在于一在字。若曰在上在下。则固有两截之病。而若曰自形而上者为道。自形而下者为器。而道与器。即就形处分别云。则亦何病之有哉。迷滞之见。则终未知其为病。如何。
矣一说。正亦愚辈之所取而为据者也。愚何尝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分别道与气耶。既曰阴阳。则其已成形可知。虽以五行言之。五行之质。即形也。五行之气。即气也。至于卦爻亦然。何可谓之无形气之别耶。本义所论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夫形固是气之重浊者。则形亦同是气也。故朱子以形与气同谓之器。而若分而言之。则尤当如尤翁之说。然此非两截也。又非三层也。就已成形处。分别其道与器而已。离而言之。曰道曰器。合而言之。道亦器。器亦道。然则离合二字。亦何谓之说不得邪。朱子所谓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云者。其病在于一在字。若曰在上在下。则固有两截之病。而若曰自形而上者为道。自形而下者为器。而道与器。即就形处分别云。则亦何病之有哉。迷滞之见。则终未知其为病。如何。讲粹语心说[四]
来教云。退溪若以神气专属理。则何以有湛一气之本。气何能纯善之训耶。夫神气者。即湛一也。湛一者。即神气也。以退溪之明而岂有此矛盾哉。即此可知其本意。未必如此。退溪先生。若果以湛一指神气而言也。则何以又有气。何能纯善之训耶。夫神气者。静亦纯善。动亦纯善。而退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0L 页
 乃谓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此则分明以血气言。而非指神气言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退溪乃以理发气发。相对言之。则此非以理兼神气看。而与血气对举说者乎。若以上下语意之矛盾。为非退溪本意之證。则以湛一为神气。而其又即云气何能纯善者。独不为矛盾之言邪。愿更详之。
乃谓惟是气。未用事时。理为主。故纯善耳。此则分明以血气言。而非指神气言也。发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退溪乃以理发气发。相对言之。则此非以理兼神气看。而与血气对举说者乎。若以上下语意之矛盾。为非退溪本意之證。则以湛一为神气。而其又即云气何能纯善者。独不为矛盾之言邪。愿更详之。第二条。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云云。高明之所改正者。大胜于前签。但此是吾辈所独得之见也。而乃谓退溪之意如此。则恐未免牵强捏合之讥。盖退溪所谓主于气一句意。决非杂乎血气之谓也。如何。
主于理而气随之。若改以理为主。而气随之云云。来教似然矣。
第三条。在清净则理亦清净。在污贱则理亦污贱云云。来教非不好也。但栗翁所释程子言。人生气禀。理有善恶者。有不合于朱子之说。是为疑晦之端何者。语类云。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又曰。只作合字看。栗翁则乃以实理释之。此其见解。不能无异同于朱子也。且其所谓气禀有善恶。故理亦有善恶云者。其语势有似乎南塘之语。此愚之所以疑其或为初年未到之言也。然栗翁答牛溪书。亦有曰。未发之体。亦有善恶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1H 页
 可言者。甚误。又有曰。未发者。性之本然也。太极之妙也。中也大本也。于此。亦有不善之萌。则是圣人独有大本。而常人无大本也。即此数句语。可知栗谷本意。非谓理之本体。随其气质之善恶。而有所不同也。则今不须多费说话也。第四条来教云。朱子所谓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界至处。若只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矣一说。正亦愚辈之所取。以为据者也。愚何尝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而别道与器邪。噫。尤庵先生病退,沙两先生之以形与道为二。形与器为一。而以形道器看作三件物事。引中庸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及语类说形而上。全是天理。形而下。只是那渣滓。至于形。又是渣滓至浊者而为證曰。是皆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既以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而上。以器为形而下矣。此其言非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为形。而以理为形而上。以已成形者为形而下者乎。朱子所谓就形处离合分别云云。正如以形与道为二。形与气为一之论。是乃退,沙二先生之所根据而为说者也。则其与尤翁看作三件之见。大相不同。高明既主尤翁说。而自谓亦以此朱子说为据云尔。则愚之惑滋甚也。
可言者。甚误。又有曰。未发者。性之本然也。太极之妙也。中也大本也。于此。亦有不善之萌。则是圣人独有大本。而常人无大本也。即此数句语。可知栗谷本意。非谓理之本体。随其气质之善恶。而有所不同也。则今不须多费说话也。第四条来教云。朱子所谓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处离合分别。此正界至处。若只说作在上在下。便是两截矣一说。正亦愚辈之所取。以为据者也。愚何尝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而别道与器邪。噫。尤庵先生病退,沙两先生之以形与道为二。形与器为一。而以形道器看作三件物事。引中庸注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及语类说形而上。全是天理。形而下。只是那渣滓。至于形。又是渣滓至浊者而为證曰。是皆以理气形三者。分别言之。既以三者分别言之。则当以道为形而上。以器为形而下矣。此其言非以未成形之阴阳之气为形。而以理为形而上。以已成形者为形而下者乎。朱子所谓就形处离合分别云云。正如以形与道为二。形与气为一之论。是乃退,沙二先生之所根据而为说者也。则其与尤翁看作三件之见。大相不同。高明既主尤翁说。而自谓亦以此朱子说为据云尔。则愚之惑滋甚也。来教又云。既曰阴阳则其已成形可知。虽以五行言之。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1L 页
 行之质。即形也。五行之气。即气也。愚谓阴阳有已成形者。有未成形者。以太极图说。所谓阳变阴合。生水火木金土而言之。则其变合而已。生水火木金土者。固是已成形之阴阳。其在变合以前者。亦可谓之已成形者乎。以中庸注所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言之。则其化生万物以后。亦是已成形之阴阳也。其在化生万物以前者。亦可谓之已成形者乎。
行之质。即形也。五行之气。即气也。愚谓阴阳有已成形者。有未成形者。以太极图说。所谓阳变阴合。生水火木金土而言之。则其变合而已。生水火木金土者。固是已成形之阴阳。其在变合以前者。亦可谓之已成形者乎。以中庸注所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言之。则其化生万物以后。亦是已成形之阴阳也。其在化生万物以前者。亦可谓之已成形者乎。来教又云。至于卦爻亦然。何可谓之无形气之别邪。愚之前言。窃恐高明于卦爻阴阳之义。亦有所未达者。果验于此也。盖本义所谓卦爻阴阳者。谓卦爻中阴阳。而非谓卦爻与阴阳也。今高明则看作卦爻与阴阳。故先言阴阳之为已成形。而继之曰。至于卦爻。亦然云云。夫何以高明之才智。而乃有此一失耶。愿更读系辞。而密察其上下文义。则可知就卦爻上。分别形气之论。必见笑于识者也。来教又云。夫形固是气之重浊者。则形亦同是气也。故朱子以形与气。同谓之器。而若分而言之。则又当如尤翁之说云云。高明既知朱子之以形与气同谓之器。则宜不以退,沙之以形与器为一为病也。是则高明所见。亦异于尤翁也。高明又曰。若分而言之。则又当如尤翁之说。然则尤翁说其不为一义乎。大抵朱子之论。以形与器为一。而以道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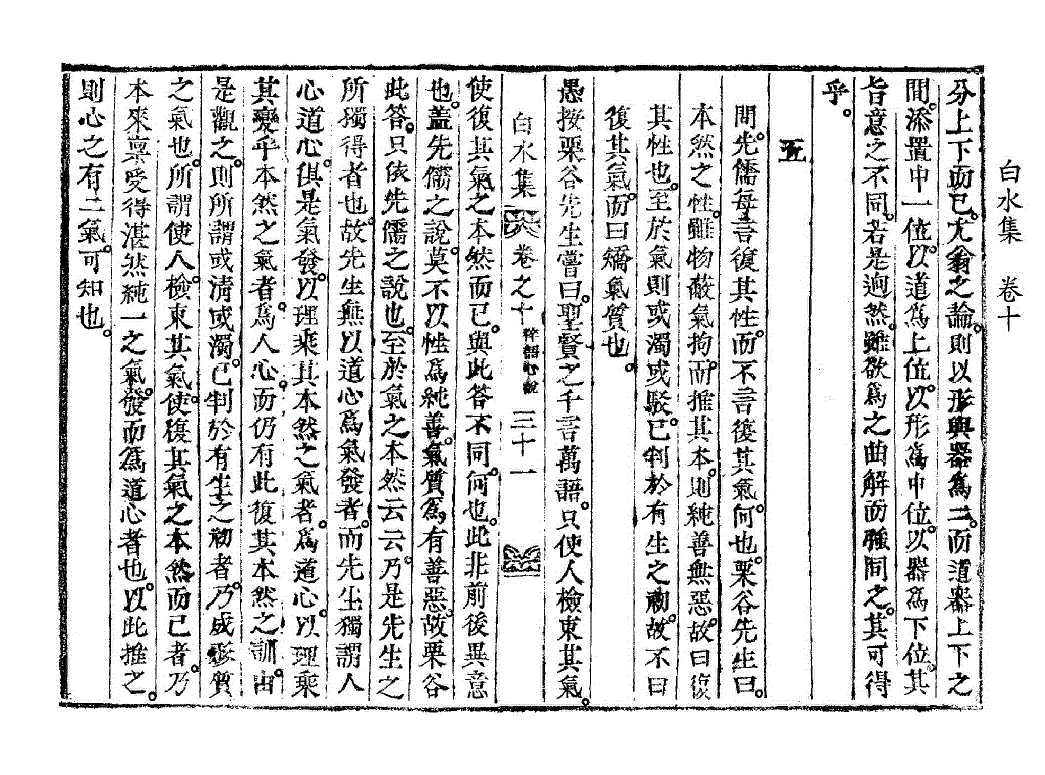 分上下而已。尤翁之论。则以形与器为二。而道器上下之间。添置中一位。以道为上位。以形为中位。以器为下位。其旨意之不同。若是迥然。虽欲为之曲解而强同之。其可得乎。
分上下而已。尤翁之论。则以形与器为二。而道器上下之间。添置中一位。以道为上位。以形为中位。以器为下位。其旨意之不同。若是迥然。虽欲为之曲解而强同之。其可得乎。讲粹语心说[五]
问。先儒每言复其性。而不言复其气。何也。栗谷先生曰。本然之性。虽物蔽气拘。而推其本。则纯善无恶。故曰复其性也。至于气则或浊或驳。已判于有生之初。故不曰复其气。而曰矫气质也。
愚按栗谷先生尝曰。圣贤之千言万语。只使人检束其气。使复其气之本然而已。与此答不同。何也。此非前后异意也。盖先儒之说。莫不以性为纯善。气质为有善恶。故栗谷此答。只依先儒之说也。至于气之本然云云。乃是先生之所独得者也。故先生无以道心为气发者。而先生独谓人心道心。俱是气发。以理乘其本然之气者。为道心。以理乘其变乎本然之气者。为人心。而仍有此复其本然之训。由是观之。则所谓或清或浊。已判于有生之初者。乃成形质之气也。所谓使人。检束其气。使复其气之本然而已者。乃本来禀受得湛然纯一之气。发而为道心者也。以此推之。则心之有二气。可知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2L 页
 尤庵先生曰。择之精而不使人心杂乎道心者。讲学之事也。守之一而不使天理流于人欲者。主敬之事也。辨人欲而克之者。讲学之要也。明天理而复之者。主敬之工也。
尤庵先生曰。择之精而不使人心杂乎道心者。讲学之事也。守之一而不使天理流于人欲者。主敬之事也。辨人欲而克之者。讲学之要也。明天理而复之者。主敬之工也。愚谓辨人欲而明天理者。讲学之要也。克之复之者。主敬之工也。尤翁之以辨人欲而克之。属之讲学。明天理而复之。属之主敬者。恐欠别白。
所谓敬者。固当行于无事存养之时。尤不可不行于有事省察之馀也。必须动静如一。然后始可言持敬之功矣。然此事静时。易为凑泊。动时易为涣散。要使一日之间。静时多而动时少。然后渐见其效矣。
要使一日之间。静时多而动时少。此一段。恐为语病。盖人伦日用之间。应接之时常多。无事之时常少。则虽欲静多动少。其可得乎。若要废事静坐。则非儒者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道也。其可乎哉。省察之馀馀字。恐际之误也。
栗谷先生语第五条。问气禀拘之于前。物欲蔽之于后。学者之用功。难于拘处。易于蔽处邪。曰。克去物欲之蔽。则气禀之拘。一时消释矣。用功。岂有二致乎。
此段可疑。如伯夷之清。初无物欲之蔽。而其气禀之偏。则有所不免。由是观之。其可谓克去物欲之蔽。则气禀之拘。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3H 页
 一时消释乎。此则分明是记者之误也。
一时消释乎。此则分明是记者之误也。问。郑圃隐仕于辛祦辛昌之朝。何也。尤庵先生曰。当时以祦昌冒姓王氏。如吕政牛睿。故圃隐亦以为王氏而事之邪。未可知也。在座者应曰。君为轻。社稷为重。为社稷而仕邪。曰。岂有无君之社稷乎。圃隐出处终始。不分明也。(语录)
按尤庵先生撰牧隐碑阴记。而其于当祦废出。牧隐谒祦于骊。又尝以迎祦为请。又尝以立前王之子为言。引用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说。则此非以牧隐为是之言乎。又 太祖即位。召牧隐至阙。以布衣自坐一处曰。老夫无坐处。尤翁以此比之伯夷。则其与牧隐为祦昌守节。为如何哉。而至论圃隐。则乃曰。圃隐出处终始。不分明也。其为祦昌之心则同。而一许一疑之。何也。是为可商量处。
退溪先生曰。真西山议论。虽时有文章气习。然其人品甚高。见理明而造诣深。朱门以后。一人而已。
愚按朱子之论人心道心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真西山则以知觉专为人心。以仁义礼智之理为道心。此其不合于朱子者。一也。朱子则以心不专属形而上下。而西山则直以心为形而上。此其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3L 页
 合于朱子者。二也。朱子曰。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西山尝论形而上形而下曰。形而上。言无极。形而下。言太极。是则以无极太极为二物也。此其不合于朱子者。三也。由是观之。则退翁之以见理明造诣深。朱门以后一人许之者。恐涉太过矣。
合于朱子者。二也。朱子曰。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西山尝论形而上形而下曰。形而上。言无极。形而下。言太极。是则以无极太极为二物也。此其不合于朱子者。三也。由是观之。则退翁之以见理明造诣深。朱门以后一人许之者。恐涉太过矣。漫笔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媒。注云。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但谓简狄以玄鸟至之时。祈于郊媒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郑注。乃有堕卵吞孕之事。与生民诗注所言姜嫄。履巨迹而生弃之事。皆怪妄不经。削之可也。
愚谓陈氏此说。可见其穷格之功。有所未尽也。盖人物之生。合下皆以气化。后来形化盛而气化遂息。此非可疑之事乎。然而造化自然。是乃理之常也。故先贤未尝疑之。以是推之。则形与气感。化生人物。亦非理外之事。故黄帝之生也。母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生帝。简狄之吞卵生契。姜嫄之履迹生弃。亦此类也。何可谓之怪妄不经也。
孟冬之月。命太史衅龟筴注。冯氏曰。衅龟筴者。杀牲取血而涂龟与蓍筴也。古者。器成而衅以血。所以攘却不祥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4H 页
 愚谓冯氏说误矣。何者。按朱子语类曰。古有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史记上龟筮传占春。将鸡子就上面开卦。便也是将生气去接他。便是衅龟之意。朱子之所解衅龟之义。若是明白。而冯氏不知此理。乃以攘却不祥释之。岂不误哉。而陈氏之集注。舍朱训而用冯说。则亦可见其识见之粗浅也。或曰。听子之言。则衅龟果非为攘却不祥。而衅筴之义。亦宜同然。但其所谓古者。器成而衅以血。亦非攘却不祥之意欤。曰。愚按杂记曰。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又曰。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注。长乐陈氏曰。衅者。涂衅以血。交神明之道也。由是观之。则冯氏所谓器成而衅以血者。亦恐指宗庙之器。而所谓攘却不祥一句。则乃冯氏之杜撰。而非其本义也。或又问衅庙衅器。何以为交神明之道也。曰。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复魄。立重设主。便是常要接续他些子精神。在这里。古有衅龟。用牲血云云。(见上)又曰。祭神多用血肉者。盖要得藉他之生气耳。又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也。观此数语。可知衅庙衅器之为交神明之道也。又问。鬼神藉此生气为灵者。何理也。曰。天地造化。只是阴阳变合。而生五行万物。故在
愚谓冯氏说误矣。何者。按朱子语类曰。古有衅龟用牲血。便是觉见那龟久后不灵了。又用些子生气去接续他。史记上龟筮传占春。将鸡子就上面开卦。便也是将生气去接他。便是衅龟之意。朱子之所解衅龟之义。若是明白。而冯氏不知此理。乃以攘却不祥释之。岂不误哉。而陈氏之集注。舍朱训而用冯说。则亦可见其识见之粗浅也。或曰。听子之言。则衅龟果非为攘却不祥。而衅筴之义。亦宜同然。但其所谓古者。器成而衅以血。亦非攘却不祥之意欤。曰。愚按杂记曰。成庙则衅之。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又曰。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豭豚。注。长乐陈氏曰。衅者。涂衅以血。交神明之道也。由是观之。则冯氏所谓器成而衅以血者。亦恐指宗庙之器。而所谓攘却不祥一句。则乃冯氏之杜撰。而非其本义也。或又问衅庙衅器。何以为交神明之道也。曰。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复魄。立重设主。便是常要接续他些子精神。在这里。古有衅龟。用牲血云云。(见上)又曰。祭神多用血肉者。盖要得藉他之生气耳。又曰。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也。观此数语。可知衅庙衅器之为交神明之道也。又问。鬼神藉此生气为灵者。何理也。曰。天地造化。只是阴阳变合。而生五行万物。故在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4L 页
 人则神气为阳。血气为阴。神气为主。而血为气配。能运用一身。又能助神知觉。是以医书云。目得血而能视。耳得血而能听。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朱子答或人植物无知。动物有知之问。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以是究之。则鬼神藉他血肉之生气为灵之义。可知也。夫龟筴得牲血而复灵。祭祀之鬼神。藉血肉之生气而为灵。则天地本然。神气之在人者。得血气而生知觉。此非一理乎。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义。本自如此。而今世之儒者。知不及此。故闻我先师气亦有二之训。而莫不疑之。可叹。
人则神气为阳。血气为阴。神气为主。而血为气配。能运用一身。又能助神知觉。是以医书云。目得血而能视。耳得血而能听。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朱子答或人植物无知。动物有知之问。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以是究之。则鬼神藉他血肉之生气为灵之义。可知也。夫龟筴得牲血而复灵。祭祀之鬼神。藉血肉之生气而为灵。则天地本然。神气之在人者。得血气而生知觉。此非一理乎。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义。本自如此。而今世之儒者。知不及此。故闻我先师气亦有二之训。而莫不疑之。可叹。仪礼通解续天子出征条。引大传语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注云。文王称王早矣。于殷犹为诸侯。于是著焉。疏曰。云文王称王早矣者。土无二王。殷纣尚存。即为早。所以早称王者。案中候我应云。我称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虽于时为早。于年为晚矣。故周本记云。文王受命六年。立灵台布王号。于时称王。年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终抚诸是也。文王既称王。文王生虽称王。号称犹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5H 页
 愚按此注疏之说。虽有根据。然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义推之。文王岂有生称王之理乎。若然。孔子亦何以至德称之乎。尽信书。不如无书者。正谓此等书也。所疑勉斋于注疏说失是处。必引朱文公之言以正之。而于此独无所辨。何也。是所不能无惑也。
愚按此注疏之说。虽有根据。然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义推之。文王岂有生称王之理乎。若然。孔子亦何以至德称之乎。尽信书。不如无书者。正谓此等书也。所疑勉斋于注疏说失是处。必引朱文公之言以正之。而于此独无所辨。何也。是所不能无惑也。疑礼问解。黄宗海问知生者。吊而不伤。礼意固当。而于朋旧相好之间。吊其母丧而不哭。此果人情乎。沙溪先生曰。妇人之丧。未及升堂者。不哭可也。乡人多有哭之者。非是。
愚未详此问答之意。窃以为不哭。何当于吊而不伤之义乎。后闻洛中所谓知礼之士。吊其朋旧之遭内艰者。主人虽哭而吊者不哭。问其故。则曰此是伤而不吊。吊而不伤之义也。余于是。始知问解问答之意如此。而今之所谓知礼者。皆依问解之言而行之也。因遂起疑曰。礼所谓知死而不知生。则伤而不吊。知生而不知死。则吊而不伤者。盖谓知死者。而不知丧人。则只哭灵位。而不哭丧人。知生者而不知亡人。则只哭丧人而不哭灵位也。今以死者之不知。而于丧人亦不哭。则恐非吊而不伤之本义也。朋友丧明。犹且哭之。而况丧其亲乎。乃遍考礼书。则其在曲礼注曰。吊伤。皆致命辞也。杂记。诸侯使人吊辞曰。寡君闻君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5L 页
 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伤辞未闻也。说者有吊辞云。皇天降灾。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于死者。盖本伤辞。辞毕。退皆哭。其在通典。亦曰。有吊宾。主人迎中门外。拜宾。宾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位。众随入。知生者吊。知死者伤。主人哭。吊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门外如初。吊辞至主人前。曰云云。伤辞诣丧前。曰云云。各主于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伤而且吊也。按此两条之言。伤吊之义。既详且备。而一则曰辞毕退皆哭。一则曰主人哭。吊者皆哭而已。未尝有知死者哭。知生者不哭之言。则此与问解问答之语。今日所行之事。岂不大相径庭乎。愚于是益信朱子所谓如其可疑。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者。实为万世不可易之正论。窃观近世礼家之行礼。多失古礼之本义者。故姑举此一端。欲令后贤知所审择也。
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于生者。伤辞未闻也。说者有吊辞云。皇天降灾。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于死者。盖本伤辞。辞毕。退皆哭。其在通典。亦曰。有吊宾。主人迎中门外。拜宾。宾不答拜。主人入。即堂下位。众随入。知生者吊。知死者伤。主人哭。吊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门外如初。吊辞至主人前。曰云云。伤辞诣丧前。曰云云。各主于其所知也。若有知生又知死者。伤而且吊也。按此两条之言。伤吊之义。既详且备。而一则曰辞毕退皆哭。一则曰主人哭。吊者皆哭而已。未尝有知死者哭。知生者不哭之言。则此与问解问答之语。今日所行之事。岂不大相径庭乎。愚于是益信朱子所谓如其可疑。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者。实为万世不可易之正论。窃观近世礼家之行礼。多失古礼之本义者。故姑举此一端。欲令后贤知所审择也。河图以奇偶之数。示阴阳对待交合生成之理。又以示五行循环相生之妙也。洛书以奇数。示五行迭运生生不穷之理。又以示五行循环相克之妙也。是知二图。不可相无。而蔡九峰所谓象非偶不立。数非奇不行。朱夫子所谓河图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洛书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复克水者。可谓得其宗旨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6H 页
 问。先天图有自然之象数。伏羲当初。亦知其然否。朱子曰。也不见得如何。但横图据见在底。画较自然。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做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画底。伏羲当初。也只见太极下面。有个阴阳。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去。做成这物事。不觉成来却如此齐整。
问。先天图有自然之象数。伏羲当初。亦知其然否。朱子曰。也不见得如何。但横图据见在底。画较自然。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做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不甚依他元初画底。伏羲当初。也只见太极下面。有个阴阳。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去。做成这物事。不觉成来却如此齐整。愚于此段。不能无疑。盖横图者。伏羲以阴阳奇偶推演出卦画来者也。圆图者。又以卦画明阴阳消长循环之理也。二图立设之本义。各有所主。而莫非出于自然。初非就方图而截作圆图也。而朱夫子乃以为圆图便是就这中间。拗做两截。恁地转来底是奇。恁地转去底是偶。有些造作云云。窃恐伏羲分立两图之意。则不如是。恨未及就正于紫阳门下也。
问。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实然之理。犹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为一物。其德自为德。侯氏解鬼神之为德。谓鬼神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为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为德。不成说。中庸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为形而上者。
梁恭伯以本心为形而下之器。而以明德为心中所具之理。又论仁者。本心之全德。而以本心与德。每每分别言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6L 页
 则其论正如侯氏之论。鬼神之德相似。盍观此朱子驳正之说乎。
则其论正如侯氏之论。鬼神之德相似。盍观此朱子驳正之说乎。尤庵先生答郑景由曰。所谓所得乎天。统言心性情三者。而今单言性。然则心与情。独非得于天者耶。其答沈明仲书。亦然。
梁恭伯每以所得乎天一句。而谓明德。专指性言。其所见。正与郑景由,沈明仲一般。若观此尤翁断案。则渠必落胆矣。
朱子曰。心如个宝珠。气如水。若水清则宝珠在那里。也莹澈光明。若水浊则和那宝珠也。昏浊了。
梁恭伯则以本心谓如水。明德谓如宝珠。何其与朱子说。不同也。
尤庵答金起之曰。意不诚。是好善恶恶之心不诚。故谓之私过。至于正心地位。则虽无私欲恶念。而其乍往乍来。閒思浮念。亦害于心。然非私欲恶念之比。故谓之公过。所谓心之所以不得其正。亦由于私恶之念勃勃而动其心云者。此盖问者之意以为意发于心。意当听命于心。而今曰意诚而心正。则是意反管束乎心。其序似倒云云。故先生所答之意以为意未诚而邪恶之念勃勃而动。则足以反动其心云尔。如此则意虽出于心。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7H 页
 反以动其心也。非谓意既诚后。复有邪恶之念动其心也。更看语类本文。则晓然矣。又先生以正心为戒惧。诚意属慎独者。尤为分晓。观于中庸章句。于戒惧云存天理。于慎独云遏人欲。则可知矣。
反以动其心也。非谓意既诚后。复有邪恶之念动其心也。更看语类本文。则晓然矣。又先生以正心为戒惧。诚意属慎独者。尤为分晓。观于中庸章句。于戒惧云存天理。于慎独云遏人欲。则可知矣。又曰。意诚之后。此心犹不能无乍往乍来。若存若亡之病。此虽与私欲恶念有间。而亦归于仰面贪看乌。回头错应人之患矣。故必须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然后可免此患。故章句引用敬直字。可谓深切著明矣。
使梁恭伯观此尤翁两条说。则或可觉其意诚后无复正心工夫之论之为误邪。
李君辅问传文用一边辨疑通考朱克履曰。传言所以正心之道。专以用言。退溪谓正得其意。而语类经文诚正条。既曰。心又是该动静。传文正心条。又曰。心包体用而言。传之明德章。顾諟天之明命注。朱子曰。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应接。此理亦随处发见。卢玉溪曰。日用动静语默之间。孰非顾諟明命之所。东阳许氏曰。顾諟动静皆顾。朱克履说。与语类及朱子注,卢,许二氏说皆不同。而退溪是之者。何也。尤庵答。吾于此思量不透。而欲质于朋友者。久矣。讲义曰。心之本体。可致其虚而无不正矣。于或问则曰。心之本体。物不能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7L 页
 动而无不正矣。此则似指体而言。至于章句曰。欲动情胜。而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分明主用而言也。愚恐讲义或问与章句。各是一义。恐不可牵合为一。而乃曰。经文兼体用言。传文单言用云。则窃不能深信也。朱子尝曰。惟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孔孟教人。多从发处说。据此则经传本义。皆主于用。而讲义或问。恐是推本而言之意也。盖体不得其正。则用何以得其正乎。然未发之体。恐不可以正不正为言也。此有所不敢知耳。
动而无不正矣。此则似指体而言。至于章句曰。欲动情胜。而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分明主用而言也。愚恐讲义或问与章句。各是一义。恐不可牵合为一。而乃曰。经文兼体用言。传文单言用云。则窃不能深信也。朱子尝曰。惟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孔孟教人。多从发处说。据此则经传本义。皆主于用。而讲义或问。恐是推本而言之意也。盖体不得其正。则用何以得其正乎。然未发之体。恐不可以正不正为言也。此有所不敢知耳。又曰。正心章。只言不正之病。而无正之之法。朱子论其病痛。无如所谓身在于此而心驰于彼。血肉之躯。无所管摄。其不为仰面贪看乌。回头错应人者。而此皆以用而言也。所谓心之本体。可致其虚者。正是指体。而所谓无不正。则岂不可以用而言耶。其下所谓心得其正者。正用传文所谓四不得其正也。经传之文。实无言体。而朱子急于晓人。必先从本源说来。然至于传文或问。则欲得其正意。故遂单言用而不及体。其意可见矣。
使梁恭伯见此。则亦可自知其心之体用。俱不得其正之说。为非也。
栗谷先生答牛溪书曰。未发之体。亦有善恶之可言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8H 页
 甚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大本也。安有善恶之可言耶。众人之心。不昏昧则必散乱。大本不立。故不可谓之中也。幸于一瞬之间。或有未发之时。则即此未发之时。全体湛然。与圣人不异矣。惟其瞥然之际。还失其体。昏乱随之。故不得其中耳。其所以昏且乱者。由其拘于气质故也。若曰。拘于气质而不能立大本。则可也。若曰。未发之时。亦有恶之萌兆。则大不可。盖其或昏昧。或散乱者。不可谓之未发。
甚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大本也。安有善恶之可言耶。众人之心。不昏昧则必散乱。大本不立。故不可谓之中也。幸于一瞬之间。或有未发之时。则即此未发之时。全体湛然。与圣人不异矣。惟其瞥然之际。还失其体。昏乱随之。故不得其中耳。其所以昏且乱者。由其拘于气质故也。若曰。拘于气质而不能立大本。则可也。若曰。未发之时。亦有恶之萌兆。则大不可。盖其或昏昧。或散乱者。不可谓之未发。栗谷此说。梁恭伯宜已见之。而犹以昏昧散乱。为未发前。心不得其正之病。韩南塘亦必见之。而犹以为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吾未知其何故也。
论语。七十从心所欲。不踰矩注。胡氏曰。圣人之教。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云云。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极好。尽用子细玩味。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日用之间。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来。
如使本心有善恶种子。果如南塘说。则胡,朱两先生之论。何以如此耶。
栗谷先生曰。圣贤之千言万语。只使人检束其气。使复其气之本然而已。
气之本然。若有善恶种子。而圣愚不同。则栗谷何以有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8L 页
 复其气之本然而已之训耶。
复其气之本然而已之训耶。栗谷先生又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
由是观之。则所以为人心之气。谓之圣凡不同可也。所以为道心之气。亦可谓之圣凡不同乎。
栗谷又曰。发道心者。气也。而非性命则道心不生。原人心者。理也。而非形气则人心不生。此所以或原或生公私之异者也。道心纯是天理。故有善而无恶。人心也有天理也。有人欲。故有善有恶。如当食而食。当衣而衣。圣贤所不免。此则天理也。因食色之念而流而为恶者。此则人欲也。道心只可守之而已。人心易流于人欲。故虽善必危。治心者。于一念之发。知其为道心。则扩而充之。知其为人心。则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每听命于道心。则人心亦为道心矣。何理之不存。何欲之不遏乎。
噫。栗翁此说。真得千圣之心法也。盖发道心者。本然之气也。故纯善无恶。发人心者。变乎本然之气也。故易流于人欲。纯善无恶。故曰道心。只可守之而已。又曰。扩而充之。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9H 页
 流于人欲。故曰人心虽善。必危。又曰。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每听命于道心。如此教人。然后乃可使学者。知吾心之本善。而又知所以复善之道也。彼南塘。反以心气为有善恶。而圣凡不同。此非但不知道心之纯善。亦不知人心之本善也。
流于人欲。故曰人心虽善。必危。又曰。精而察之。必以道心节制。而人心每听命于道心。如此教人。然后乃可使学者。知吾心之本善。而又知所以复善之道也。彼南塘。反以心气为有善恶。而圣凡不同。此非但不知道心之纯善。亦不知人心之本善也。北溪陈氏曰。心之动。是乘气。其曰活曰灵曰神曰妙。是因理与气合。(北溪说止此。)明德。即是虚灵神妙之活物。则何可不谓之合理气之物乎。栗谷圣学辑要养气章。以孟子牛山章。并录于养志气条。牛山章所谓仁义之心。便是明德。而栗谷并录于养气章。其意亦可见也。
圣学辑要养气章。以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章。牛山章及论浩然之气云云段。为专言养志气。以论语君子有三戒章。子之所慎齐战疾章及易慎言语节饮食之辞。为兼言养血气。而其按说曰。仁义之心。人所同受。而资禀有开蔽。真元之气。人所同有。而血气有虚实。善养仁义之心。则蔽可开而全其天矣。善养真元之气。则虚可实而保其命矣。其养之之术。亦非外假他物。只是无所挠损而已。天地之气化。生生不穷。无一息之停。人之气与天地相通。故良心真气。亦与之俱长。惟其戕害多端。所长不能胜其所消。展转牿亡。故心为禽兽。气至夭札。可不惧哉。栗翁之分言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十 第 249L 页
 气与真元之气。若是丁宁。则人身之有二气。可知也。
气与真元之气。若是丁宁。则人身之有二气。可知也。西山真氏曰。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其心本无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违仁之时。能克去私欲。则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觉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盖圆外窍中者。是心之体。(谓形质也。此乃血肉之心。)虚灵知觉者。是心之灵。(灵谓精爽也。言其妙则谓神明不测。)仁义礼智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觉属气。凡能识痛痒。识利害。识义理者。皆是也。(此所谓人心也。)若仁义智信。纯是义理。(此所谓道心也。)人能克去私欲。则所知觉者。皆义理。不能克去私欲。则所知觉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纯是理即是不违仁。杂以私欲。便是违仁。(愚按此说有病。以知觉为人心。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心者。与罗整庵以人心道心作体用看之。其失同也。且既曰心者。指知觉而言。仁义礼智信。是心之理。又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心。此心字。独非指知觉者乎。前后之言。自相矛盾也。○西山真氏又曰。形而上。言无极。形而下。言太极。此说亦不是。若如其说。则太极是气也。非理也。)
礼记礼运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此说甚好。以此言心可也。而秀气二字。易以精英。则其于心之妙。可谓竭尽无馀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