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辨
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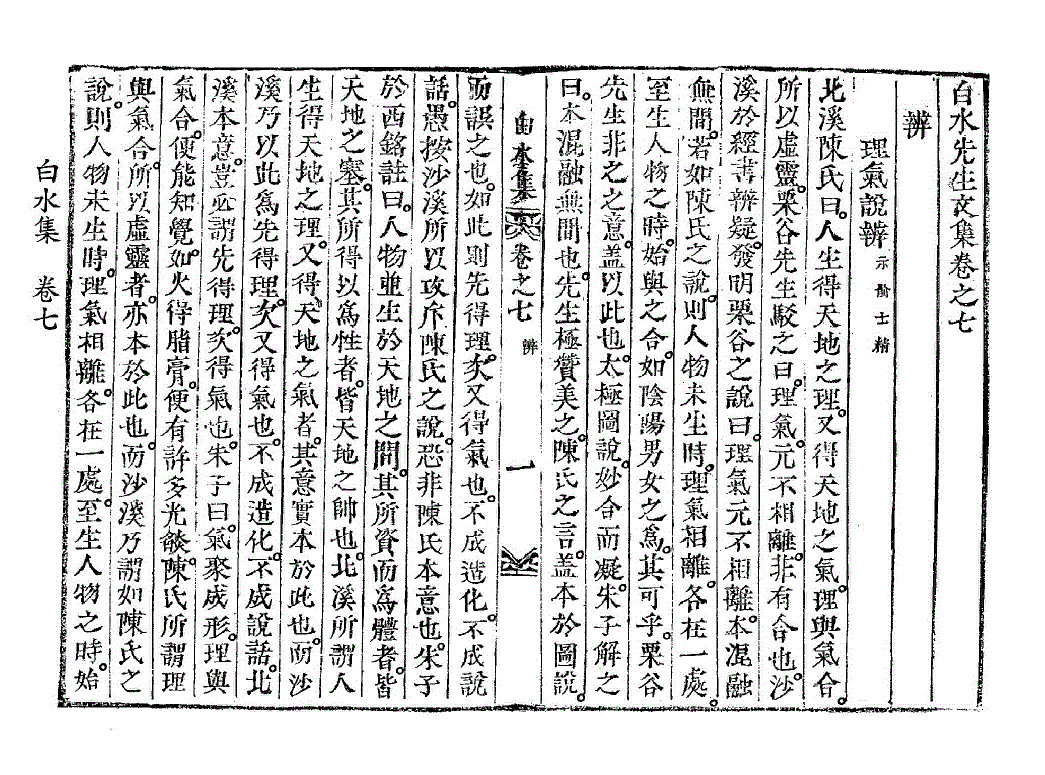 理气说辨(示俞士精)
理气说辨(示俞士精)北溪陈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气。理与气合。所以虚灵。栗谷先生驳之曰。理气。元不相离。非有合也。沙溪于经书辨疑。发明栗谷之说曰。理气元不相离。本混融无间。若如陈氏之说。则人物未生时。理气相离。各在一处。至生人物之时。始与之合。如阴阳男女之为。其可乎。栗谷先生非之之意。盖以此也。太极图说。妙合而凝。朱子解之曰。本混融无间也。先生极赞美之。陈氏之言。盖本于图说。而误之也。如此则先得理。次又得气也。不成造化。不成说话。愚按沙溪所以攻斥陈氏之说。恐非陈氏本意也。朱子于西铭注曰。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而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北溪所谓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气者。其意实本于此也。而沙溪乃以此为先得理。次又得气也。不成造化。不成说话。北溪本意。岂必谓先得理。次得气也。朱子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如火得脂膏。便有许多光燄。陈氏所谓理与气合。所以虚灵者。亦本于此也。而沙溪乃谓如陈氏之说。则人物未生时。理气相离。各在一处。至生人物之时。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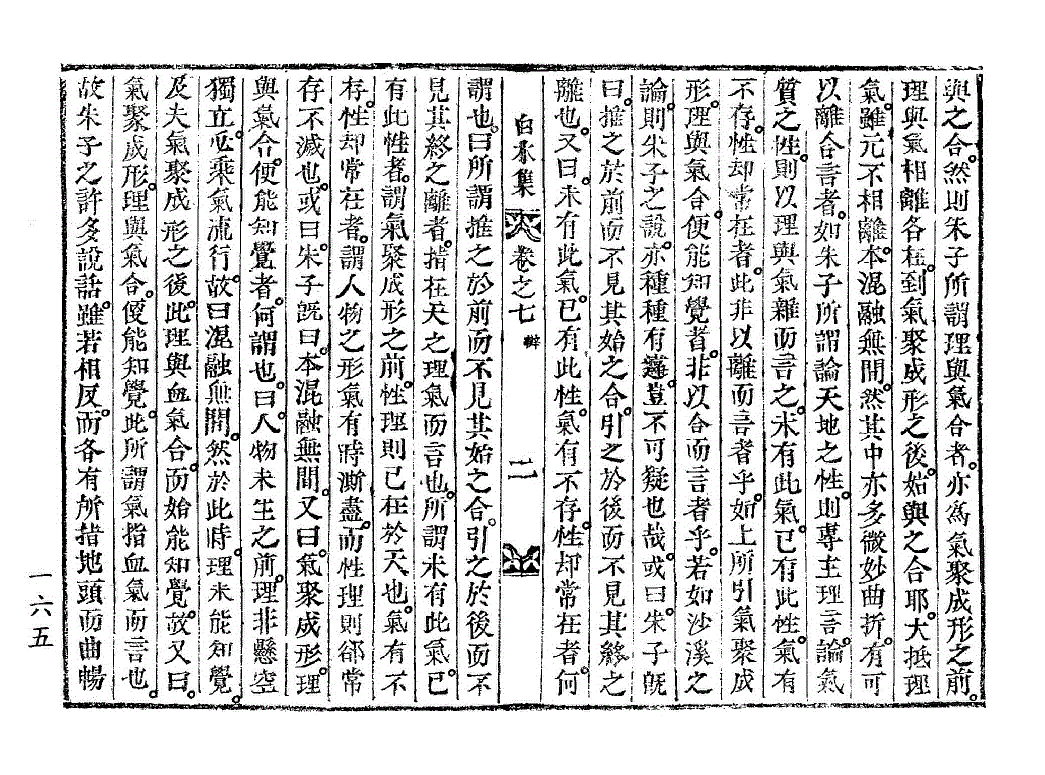 与之合。然则朱子所谓理与气合者。亦为气聚成形之前。理与气相离各在。到气聚成形之后。始与之合耶。大抵理气。虽元不相离。本混融无间。然其中亦多微妙曲折。有可以离合言者。如朱子所谓论天地之性。则专主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此非以离而言者乎。如上所引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非以合而言者乎。若如沙溪之论。则朱子之说。亦种种有违。岂不可疑也哉。或曰。朱子既曰。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又曰。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何谓也。曰所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者。指在天之理气而言也。所谓未有此气。已有此性者。谓气聚成形之前。性理则已在于天也。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谓人物之形气有时澌尽。而性理则郤常存不灭也。或曰。朱子既曰。本混融无间。又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何谓也。曰。人物未生之前。理非悬空独立。必乘气流行。故曰混融无间。然于此时。理未能知觉。及夫气聚成形之后。此理与血气合。而始能知觉。故又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此所谓气指血气而言也。故朱子之许多说话。虽若相反。而各有所指地头而曲畅
与之合。然则朱子所谓理与气合者。亦为气聚成形之前。理与气相离各在。到气聚成形之后。始与之合耶。大抵理气。虽元不相离。本混融无间。然其中亦多微妙曲折。有可以离合言者。如朱子所谓论天地之性。则专主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此非以离而言者乎。如上所引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非以合而言者乎。若如沙溪之论。则朱子之说。亦种种有违。岂不可疑也哉。或曰。朱子既曰。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也。又曰。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何谓也。曰所谓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之合。引之于后而不见其终之离者。指在天之理气而言也。所谓未有此气。已有此性者。谓气聚成形之前。性理则已在于天也。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者。谓人物之形气有时澌尽。而性理则郤常存不灭也。或曰。朱子既曰。本混融无间。又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者。何谓也。曰。人物未生之前。理非悬空独立。必乘气流行。故曰混融无间。然于此时。理未能知觉。及夫气聚成形之后。此理与血气合。而始能知觉。故又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此所谓气指血气而言也。故朱子之许多说话。虽若相反。而各有所指地头而曲畅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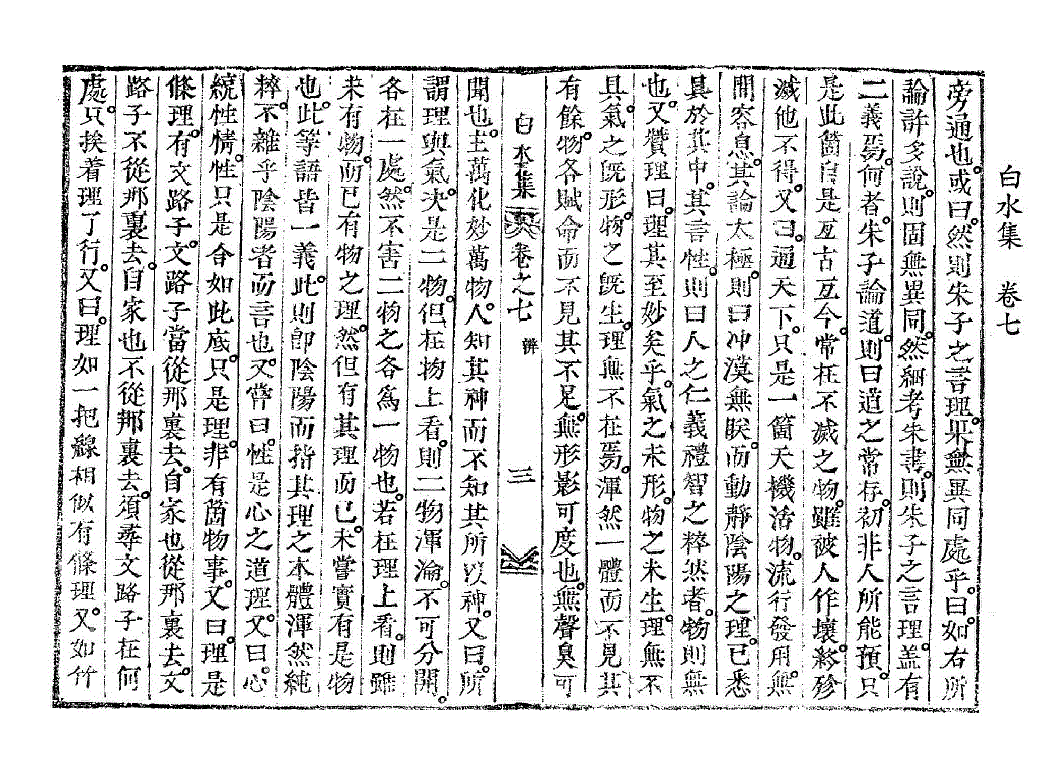 旁通也。或曰。然则朱子之言理。果无异同处乎。曰。如右所论许多说。则固无异同。然细考朱书。则朱子之言理。盖有二义焉。何者。朱子论道。则曰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又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其论太极。则曰冲漠无眹。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其言性。则曰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又赞理曰。理其至妙矣乎。气之未形。物之未生。理无不具。气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浑然一体而不见其有馀。物各赋命而不见其不足。无形影可度也。无声臭可闻也。主万化妙万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此等语皆一义。此则即阴阳而指其理之本体浑然纯粹。不杂乎阴阳者而言也。又尝曰。性是心之道理。又曰。心统性情。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又曰。理是条理。有文路子。文路子当从那里去。自家也从那里去。文路子不从那里去。自家也不从那里去。须寻文路子在何处。只挨着理了行。又曰。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又如竹
旁通也。或曰。然则朱子之言理。果无异同处乎。曰。如右所论许多说。则固无异同。然细考朱书。则朱子之言理。盖有二义焉。何者。朱子论道。则曰道之常存。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又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其论太极。则曰冲漠无眹。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其言性。则曰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又赞理曰。理其至妙矣乎。气之未形。物之未生。理无不具。气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浑然一体而不见其有馀。物各赋命而不见其不足。无形影可度也。无声臭可闻也。主万化妙万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此等语皆一义。此则即阴阳而指其理之本体浑然纯粹。不杂乎阴阳者而言也。又尝曰。性是心之道理。又曰。心统性情。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个物事。又曰。理是条理。有文路子。文路子当从那里去。自家也从那里去。文路子不从那里去。自家也不从那里去。须寻文路子在何处。只挨着理了行。又曰。理如一把线相似有条理。又如竹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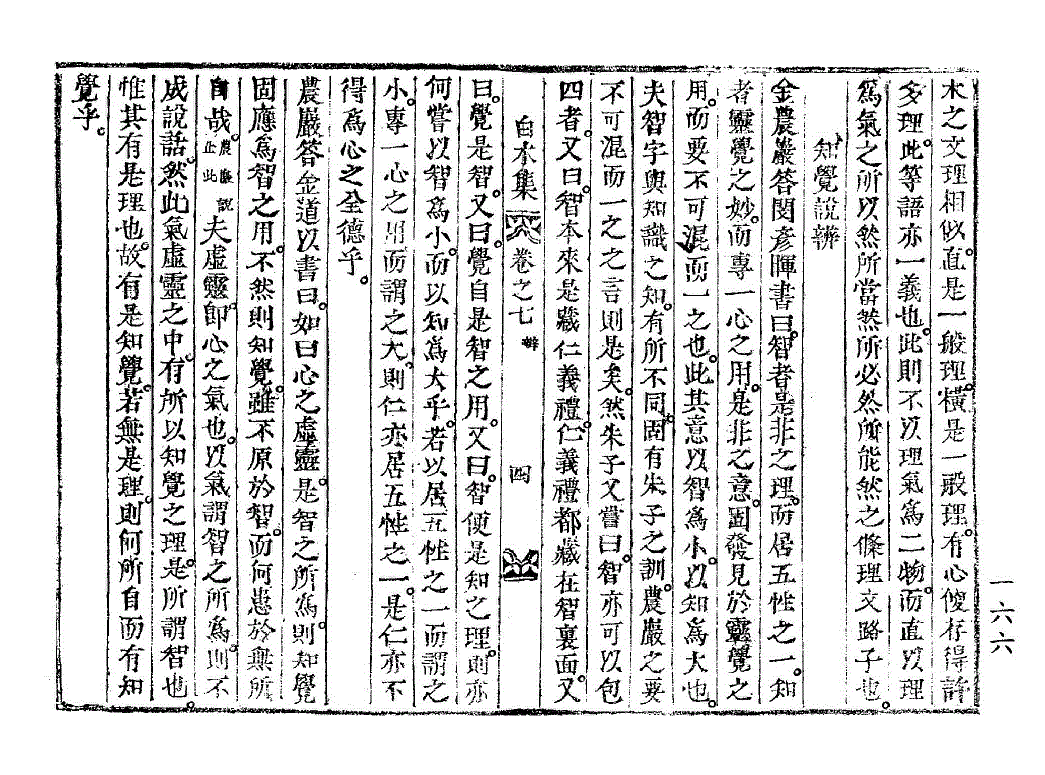 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许多理。此等语亦一义也。此则不以理气为二物。而直以理为气之所以然所当然所必然所能然之条理文路子也。
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横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许多理。此等语亦一义也。此则不以理气为二物。而直以理为气之所以然所当然所必然所能然之条理文路子也。知觉说辨
金农岩答闵彦晖书曰。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灵觉之妙。而专一心之用。是非之意。固发见于灵觉之用。而要不可混而一之也。此其意以智为小。以知为大也。夫智字与知识之知。有所不同。固有朱子之训。农岩之要不可混而一之之言则是矣。然朱子又尝曰。智亦可以包四者。又曰。智本来是藏仁义礼。仁义礼都藏在智里面。又曰。觉是智。又曰。觉自是智之用。又曰。智便是知之理。则亦何尝以智为小。而以知为大乎。若以居五性之一而谓之小。专一心之用而谓之大。则仁亦居五性之一。是仁亦不得为心之全德乎。
农岩答金道以书曰。如曰心之虚灵。是智之所为。则知觉固应为智之用。不然则知觉。虽不原于智。而何患于无所自哉。(农岩说止此)夫虚灵。即心之气也。以气谓智之所为。则不成说话。然此气虚灵之中。有所以知觉之理。是所谓智也。惟其有是理也。故有是知觉。若无是理。则何所自而有知觉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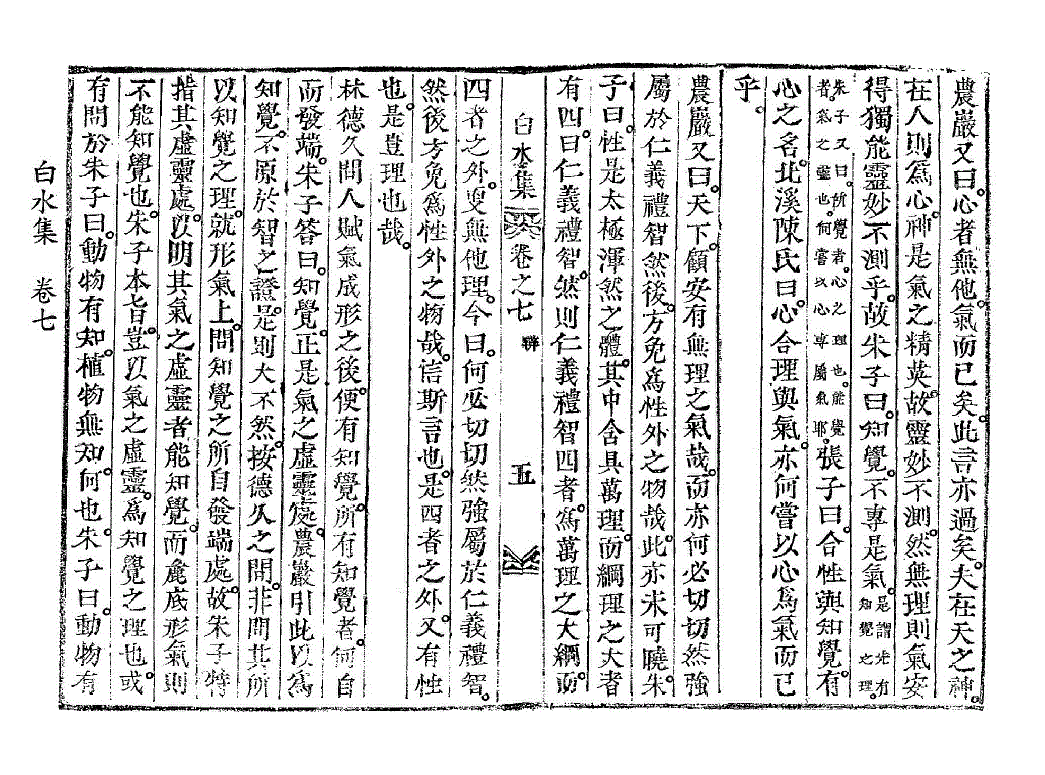 农岩又曰。心者无他。气而已矣。此言亦过矣。夫在天之神。在人则为心。神是气之精英。故灵妙不测。然无理则气安得独能灵妙不测乎。故朱子曰。知觉。不专是气。(是谓先有知觉之理。朱子又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何尝以心专属气耶。)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北溪陈氏曰。心合理与气。亦何尝以心为气而已乎。
农岩又曰。心者无他。气而已矣。此言亦过矣。夫在天之神。在人则为心。神是气之精英。故灵妙不测。然无理则气安得独能灵妙不测乎。故朱子曰。知觉。不专是气。(是谓先有知觉之理。朱子又曰。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何尝以心专属气耶。)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北溪陈氏曰。心合理与气。亦何尝以心为气而已乎。农岩又曰。天下。顾安有无理之气哉。而亦何必切切然强属于仁义礼智然后。方免为性外之物哉。此亦未可晓。朱子曰。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曰仁义礼智。然则仁义礼智四者。为万理之大纲。而四者之外。更无他理。今曰。何必切切然强属于仁义礼智。然后方免为性外之物哉。信斯言也。是四者之外。又有性也。是岂理也哉。
林德久问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所有知觉者。何自而发端。朱子答曰。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农岩引此以为知觉。不原于智之證。是则大不然。按德久之问。非问其所以知觉之理。就形气上。问知觉之所自发端处。故朱子特指其虚灵处。以明其气之虚灵者。能知觉。而粗底形气则不能知觉也。朱子本旨。岂以气之虚灵。为知觉之理也。或有问于朱子曰。动物有知。植物无知。何也。朱子曰。动物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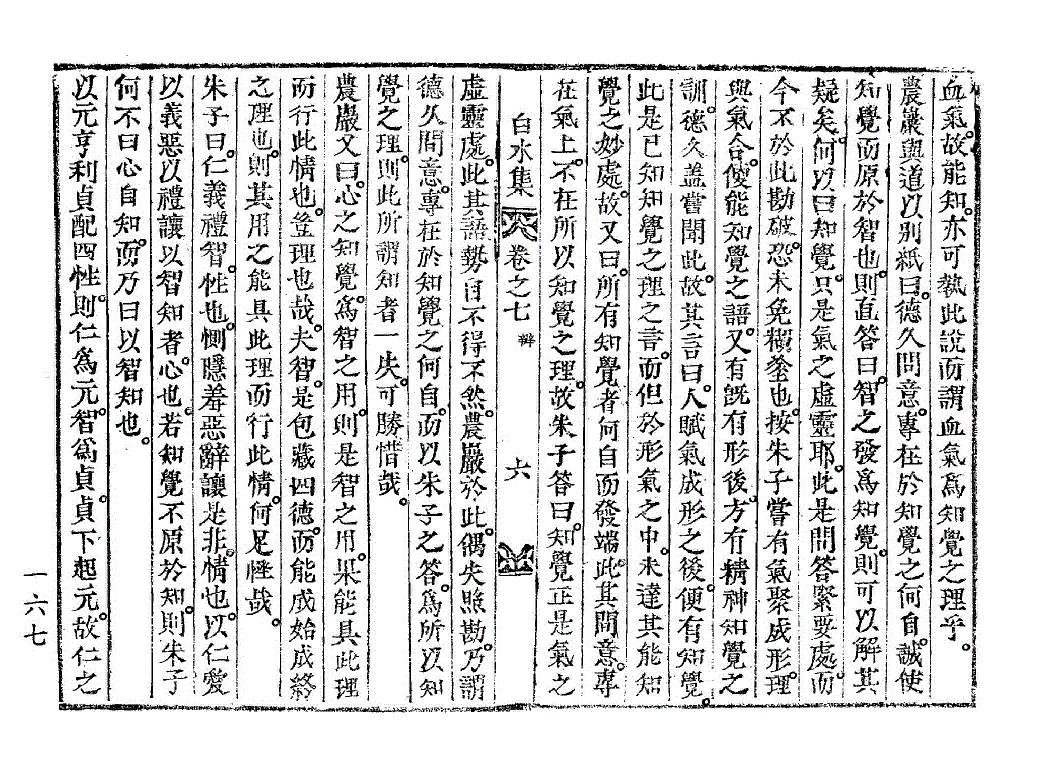 血气。故能知。亦可执此说而谓血气为知觉之理乎。
血气。故能知。亦可执此说而谓血气为知觉之理乎。农岩与道以别纸曰。德久问意。专在于知觉之何自。诚使知觉而原于智也。则直答曰。智之发为知觉。则可以解其疑矣。何以曰知觉。只是气之虚灵耶。此是问答紧要处。而今不于此勘破。恐未免糊涂也。按朱子尝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之语。又有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之训。德久盖尝闻此。故其言曰。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此是已知知觉之理之言。而但于形气之中。未达其能知觉之妙处。故又曰。所有知觉者何自而发端。此其问意。专在气上。不在所以知觉之理。故朱子答曰。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此其语势自不得不然。农岩于此。偶失照勘。乃谓德久问意。专在于知觉之何自。而以朱子之答。为所以知觉之理。则此所谓知者一失。可胜惜哉。
农岩又曰。心之知觉。为智之用。则是智之用。果能具此理而行此情也。岂理也哉。夫智。是包藏四德。而能成始成终之理也。则其用之能具此理而行此情。何足怪哉。
朱子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若知觉不原于知。则朱子何不曰心自知。而乃曰以智知也。
以元亨利贞配四性。则仁为元。智为贞。贞下起元。故仁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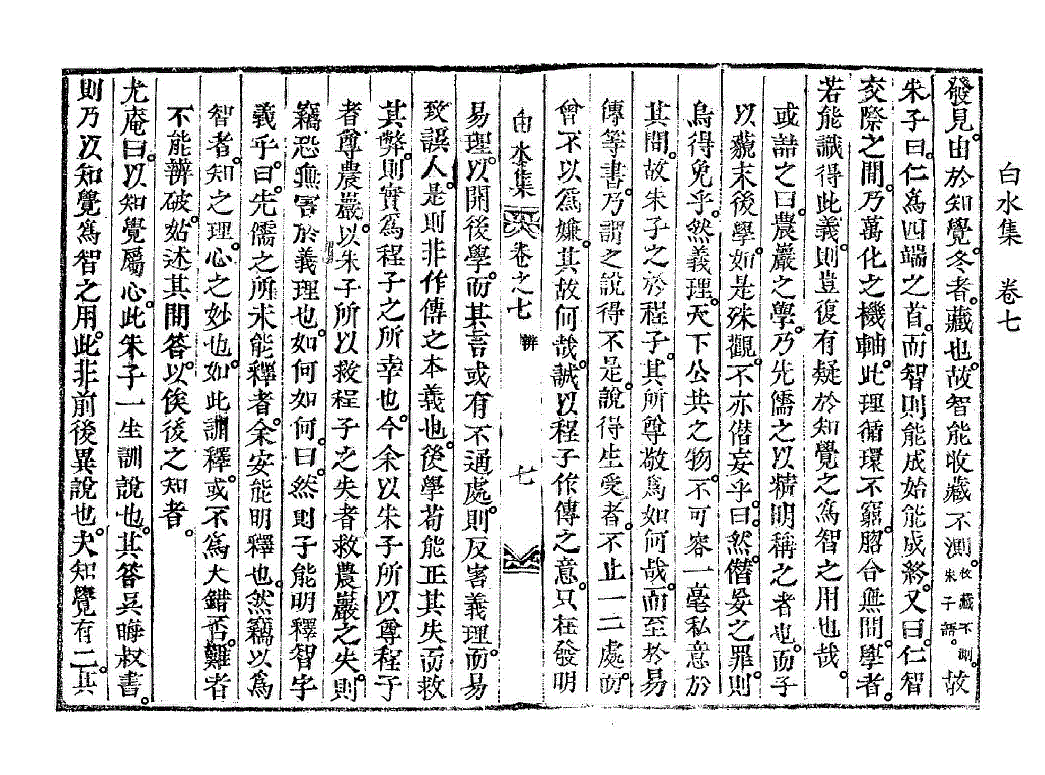 发见。由于知觉。冬者。藏也。故智能收藏不测。(收藏不测。朱子语。)故朱子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又曰。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学者。若能识得此义。则岂复有疑于知觉之为智之用也哉。
发见。由于知觉。冬者。藏也。故智能收藏不测。(收藏不测。朱子语。)故朱子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又曰。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学者。若能识得此义。则岂复有疑于知觉之为智之用也哉。或诘之曰。农岩之学。乃先儒之以精明称之者也。而子以藐末后学。如是殊观。不亦僭妄乎。曰。然。僭妄之罪。则乌得免乎。然义理。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容一毫私意于其间。故朱子之于程子。其所尊敬为如何哉。而至于易传等书。乃谓之说得不是。说得生受者。不止一二处。而曾不以为嫌。其故何哉。诚以程子作传之意。只在发明易理。以开后学。而其言或有不通处。则反害义理。而易致误人。是则非作传之本义也。后学苟能正其失而救其弊。则实为程子之所幸也。今余以朱子所以尊程子者尊农岩。以朱子所以救程子之失者救农岩之失。则窃恐无害于义理也。如何如何。曰。然则子能明释智字义乎。曰。先儒之所未能释者。余安能明释也。然窃以为智者。知之理。心之妙也。如此训释。或不为大错否。难者不能辨破。姑述其问答。以俟后之知者。
尤庵曰。以知觉属心。此朱子一生训说也。其答吴晦叔书。则乃以知觉为智之用。此非前后异说也。夫知觉有二。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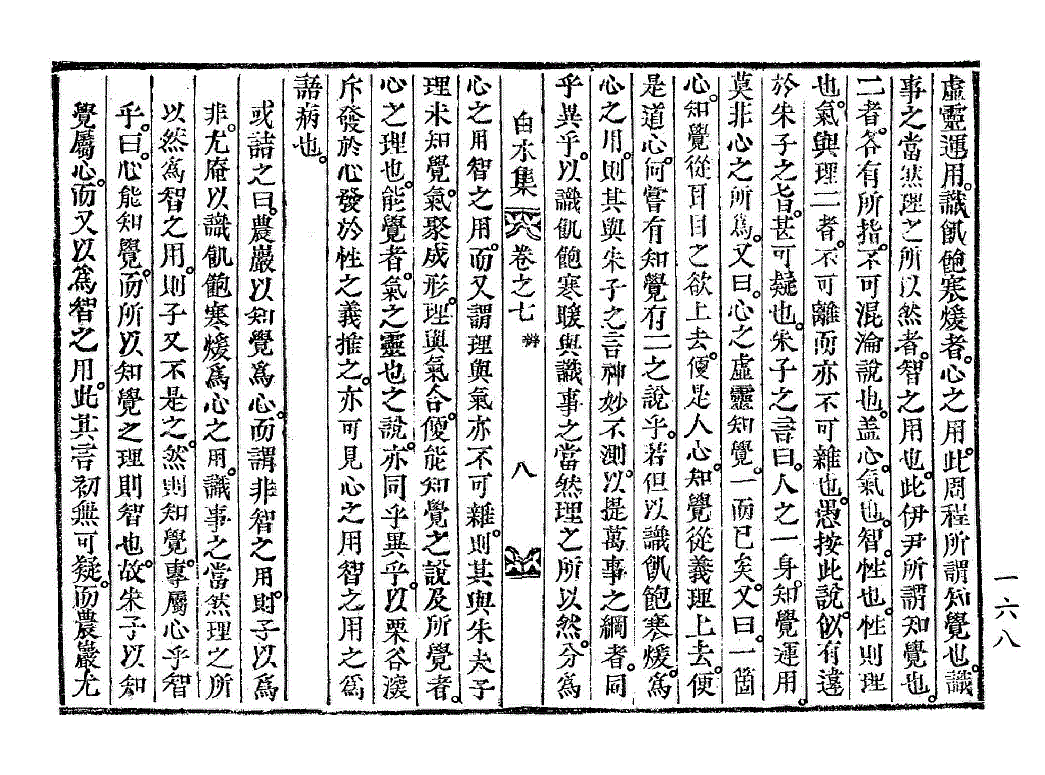 虚灵运用。识饥饱寒煖者。心之用。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盖心。气也。智。性也。性则理也。气与理二者。不可离而亦不可杂也。愚按此说。似有违于朱子之旨。甚可疑也。朱子之言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又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又曰。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何尝有知觉有二之说乎。若但以识饥饱寒煖。为心之用。则其与朱子之言神妙不测。以提万事之纲者。同乎异乎。以识饥饱寒暖与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分为心之用智之用。而又谓理与气亦不可杂。则其与朱夫子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之说及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之说。亦同乎异乎。以栗谷深斥发于心发于性之义推之。亦可见心之用智之用之为语病也。
虚灵运用。识饥饱寒煖者。心之用。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沦说也。盖心。气也。智。性也。性则理也。气与理二者。不可离而亦不可杂也。愚按此说。似有违于朱子之旨。甚可疑也。朱子之言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又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又曰。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何尝有知觉有二之说乎。若但以识饥饱寒煖。为心之用。则其与朱子之言神妙不测。以提万事之纲者。同乎异乎。以识饥饱寒暖与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分为心之用智之用。而又谓理与气亦不可杂。则其与朱夫子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之说及所觉者。心之理也。能觉者。气之灵也之说。亦同乎异乎。以栗谷深斥发于心发于性之义推之。亦可见心之用智之用之为语病也。或诘之曰。农岩以知觉为心。而谓非智之用。则子以为非。尤庵以识饥饱寒煖为心之用。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为智之用。则子又不是之。然则知觉。专属心乎智乎。曰。心能知觉。而所以知觉之理则智也。故朱子以知觉属心。而又以为智之用。此其言初无可疑。而农岩尤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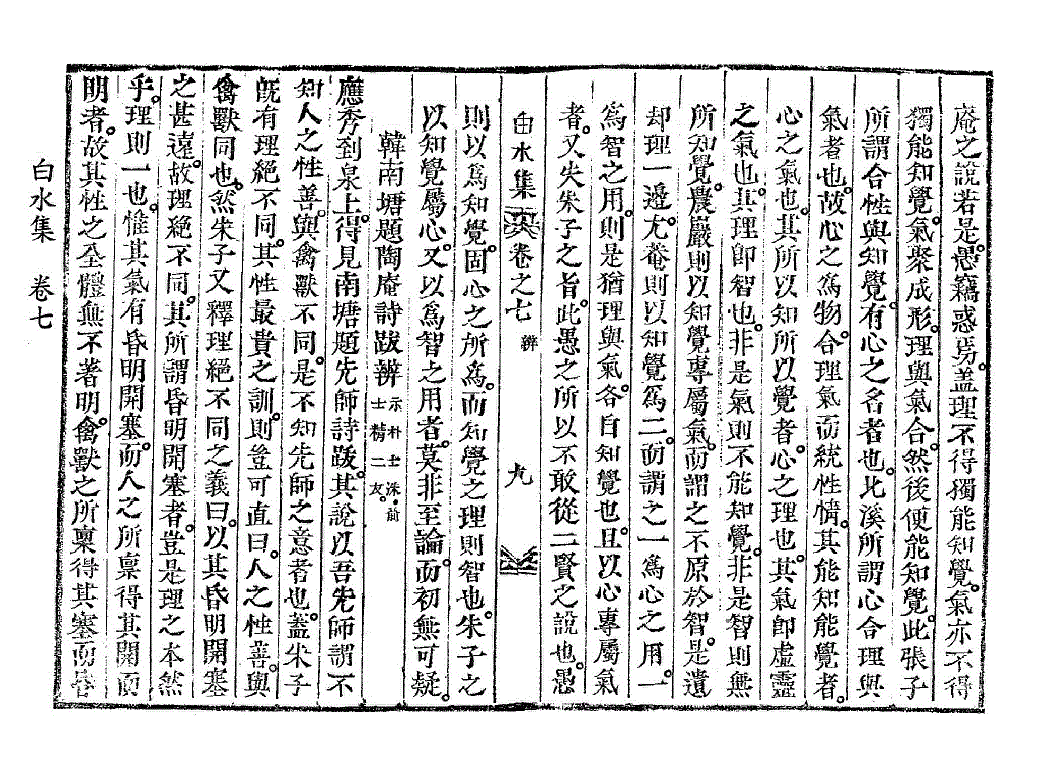 庵之说若是。愚窃惑焉。盖理不得独能知觉。气亦不得独能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然后便能知觉。此张子所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者也。北溪所谓心合理与气者也。故心之为物。合理气而统性情。其能知能觉者。心之气也。其所以知所以觉者。心之理也。其气即虚灵之气也。其理即智也。非是气则不能知觉。非是智则无所知觉。农岩则以知觉专属气。而谓之不原于智。是遗却理一边。尤庵则以知觉为二。而谓之一为心之用。一为智之用。则是犹理与气。各自知觉也。且以心专属气者。又失朱子之旨。此愚之所以不敢从二贤之说也。愚则以为知觉。固心之所为。而知觉之理则智也。朱子之以知觉属心。又以为智之用者。莫非至论。而初无可疑。
庵之说若是。愚窃惑焉。盖理不得独能知觉。气亦不得独能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然后便能知觉。此张子所谓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者也。北溪所谓心合理与气者也。故心之为物。合理气而统性情。其能知能觉者。心之气也。其所以知所以觉者。心之理也。其气即虚灵之气也。其理即智也。非是气则不能知觉。非是智则无所知觉。农岩则以知觉专属气。而谓之不原于智。是遗却理一边。尤庵则以知觉为二。而谓之一为心之用。一为智之用。则是犹理与气。各自知觉也。且以心专属气者。又失朱子之旨。此愚之所以不敢从二贤之说也。愚则以为知觉。固心之所为。而知觉之理则智也。朱子之以知觉属心。又以为智之用者。莫非至论。而初无可疑。韩南塘题陶庵诗跋辨(示朴士洙,俞士精二友。)
应秀到泉上。得见南塘题先师诗跋。其说以吾先师谓不知人之性善。与禽兽不同。是不知先师之意者也。盖朱子既有理绝不同。其性最贵之训。则岂可直曰。人之性善。与禽兽同也。然朱子又释理绝不同之义曰。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其所谓昏明开塞者。岂是理之本然乎。理则一也。惟其气有昏明开塞。而人之所禀得其开而明者。故其性之全体无不著明。禽兽之所禀得其塞而昏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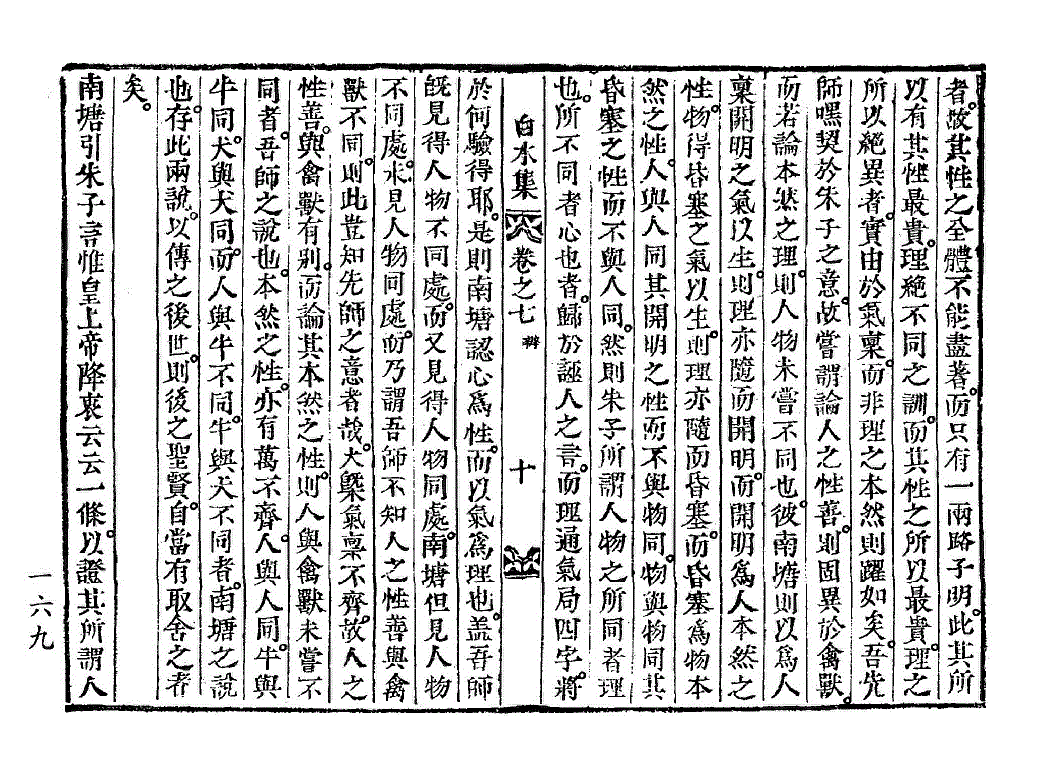 者。故其性之全体不能尽著。而只有一两路子明。此其所以有其性最贵。理绝不同之训。而其性之所以最贵。理之所以绝异者。实由于气禀。而非理之本然则跃如矣。吾先师嘿契于朱子之意。故尝谓论人之性善。则固异于禽兽。而若论本然之理。则人物未尝不同也。彼南塘则以为人禀开明之气以生。则理亦随而开明。而开明为人本然之性。物得昏塞之气以生。则理亦随而昏塞。而昏塞为物本然之性。人与人同其开明之性而不与物同。物与物同其昏塞之性而不与人同。然则朱子所谓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者。归于诬人之言。而理通气局四字。将于何验得耶。是则南塘认心为性。而以气为理也。盖吾师既见得人物不同处。而又见得人物同处。南塘但见人物不同处。未见人物同处。而乃谓吾师不知人之性善与禽兽不同。则此岂知先师之意者哉。大槩气禀不齐。故人之性善。与禽兽有别。而论其本然之性。则人与禽兽未尝不同者。吾师之说也。本然之性。亦有万不齐。人与人同。牛与牛同。犬与犬同。而人与牛不同。牛与犬不同者。南塘之说也。存此两说。以传之后世。则后之圣贤。自当有取舍之者矣。
者。故其性之全体不能尽著。而只有一两路子明。此其所以有其性最贵。理绝不同之训。而其性之所以最贵。理之所以绝异者。实由于气禀。而非理之本然则跃如矣。吾先师嘿契于朱子之意。故尝谓论人之性善。则固异于禽兽。而若论本然之理。则人物未尝不同也。彼南塘则以为人禀开明之气以生。则理亦随而开明。而开明为人本然之性。物得昏塞之气以生。则理亦随而昏塞。而昏塞为物本然之性。人与人同其开明之性而不与物同。物与物同其昏塞之性而不与人同。然则朱子所谓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者。归于诬人之言。而理通气局四字。将于何验得耶。是则南塘认心为性。而以气为理也。盖吾师既见得人物不同处。而又见得人物同处。南塘但见人物不同处。未见人物同处。而乃谓吾师不知人之性善与禽兽不同。则此岂知先师之意者哉。大槩气禀不齐。故人之性善。与禽兽有别。而论其本然之性。则人与禽兽未尝不同者。吾师之说也。本然之性。亦有万不齐。人与人同。牛与牛同。犬与犬同。而人与牛不同。牛与犬不同者。南塘之说也。存此两说。以传之后世。则后之圣贤。自当有取舍之者矣。南塘引朱子言惟皇上帝降衷云云一条。以證其所谓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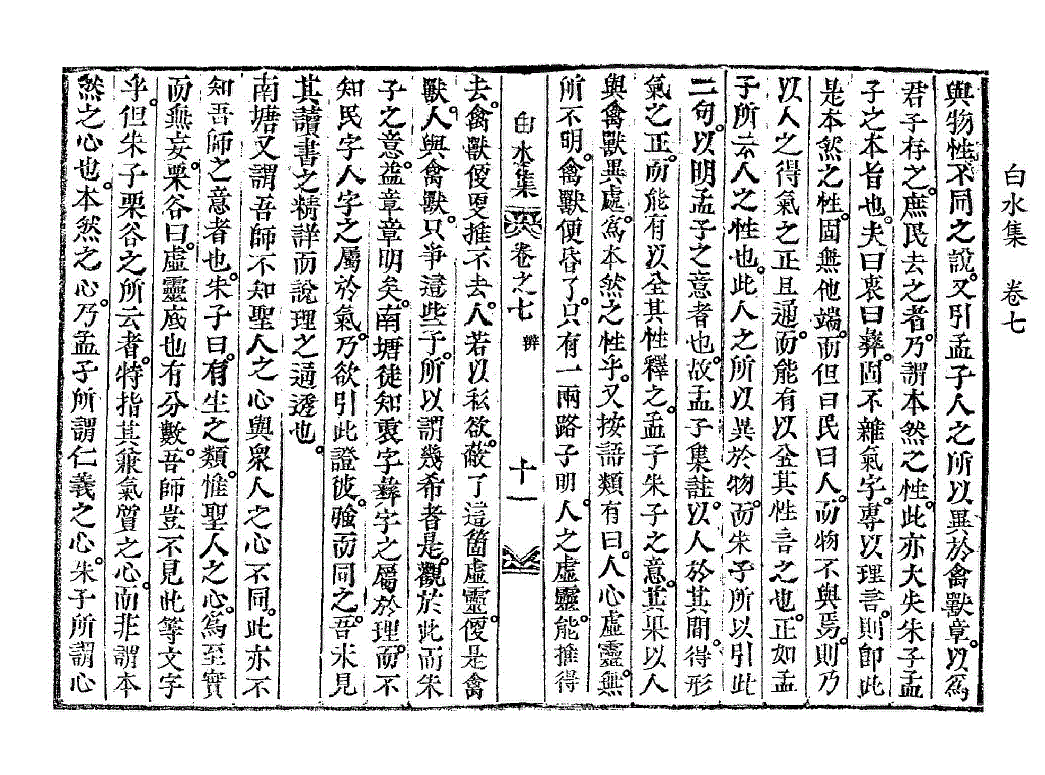 与物性不同之说。又引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以为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者。乃谓本然之性。此亦大失朱子孟子之本旨也。夫曰衷曰彝。固不杂气字。专以理言。则即此是本然之性。固无他端。而但曰民曰人。而物不与焉。则乃以人之得气之正且通。而能有以全其性言之也。正如孟子所云人之性也。此人之所以异于物。而朱子所以引此二句。以明孟子之意者也。故孟子集注。以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释之。孟子朱子之意。其果以人与禽兽异处。为本然之性乎。又按语类有曰。人心虚灵。无所不明。禽兽便昏了。只有一两路子明。人之虚灵。能推得去。禽兽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这个虚灵。便是禽兽。人与禽兽。只争这些子。所以谓几希者是。观于此而朱子之意。益章章明矣。南塘徒知衷字彝字之属于理。而不知民字人字之属于气。乃欲引此證彼。强而同之。吾未见其读书之精详而说理之通透也。
与物性不同之说。又引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章。以为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者。乃谓本然之性。此亦大失朱子孟子之本旨也。夫曰衷曰彝。固不杂气字。专以理言。则即此是本然之性。固无他端。而但曰民曰人。而物不与焉。则乃以人之得气之正且通。而能有以全其性言之也。正如孟子所云人之性也。此人之所以异于物。而朱子所以引此二句。以明孟子之意者也。故孟子集注。以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释之。孟子朱子之意。其果以人与禽兽异处。为本然之性乎。又按语类有曰。人心虚灵。无所不明。禽兽便昏了。只有一两路子明。人之虚灵。能推得去。禽兽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这个虚灵。便是禽兽。人与禽兽。只争这些子。所以谓几希者是。观于此而朱子之意。益章章明矣。南塘徒知衷字彝字之属于理。而不知民字人字之属于气。乃欲引此證彼。强而同之。吾未见其读书之精详而说理之通透也。南塘又谓吾师不知圣人之心与众人之心不同。此亦不知吾师之意者也。朱子曰。有生之类。惟圣人之心。为至实而无妄。栗谷曰。虚灵底也有分数。吾师岂不见此等文字乎。但朱子栗谷之所云者。特指其兼气质之心。而非谓本然之心也。本然之心。乃孟子所谓仁义之心。朱子所谓心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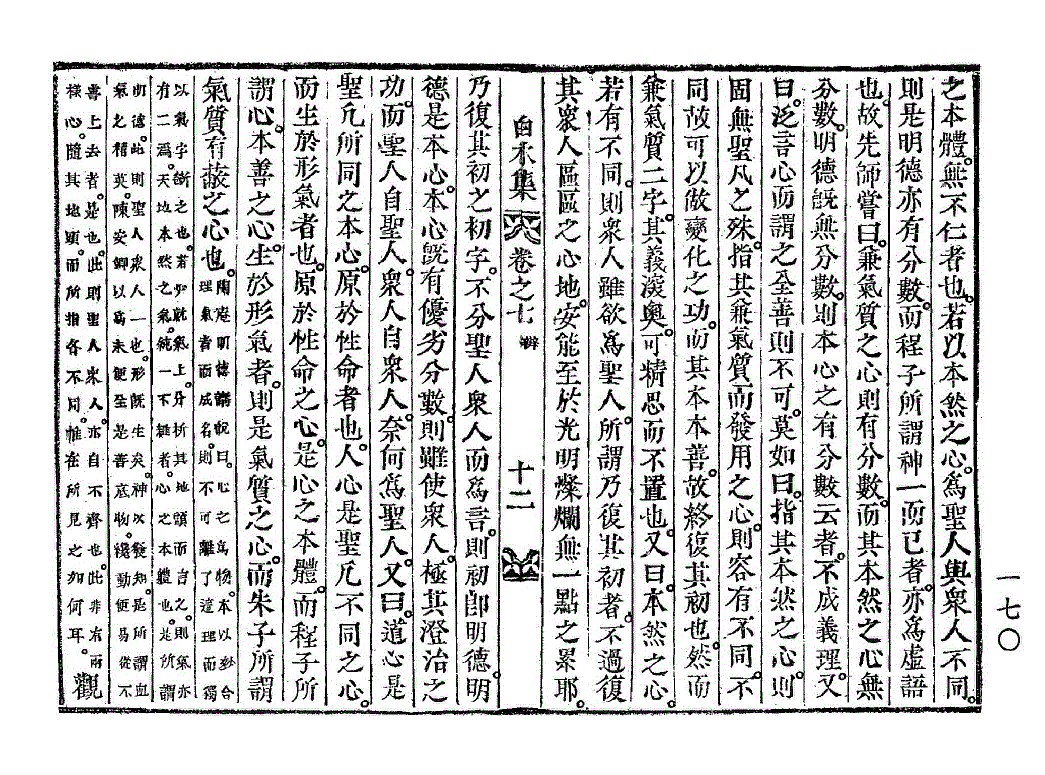 之本体。无不仁者也。若以本然之心。为圣人与众人不同。则是明德亦有分数。而程子所谓神一而已者。亦为虚语也。故先师尝曰。兼气质之心则有分数。而其本然之心无分数。明德既无分数。则本心之有分数云者。不成义理。又曰。泛言心而谓之全善则不可。莫如曰。指其本然之心。则固无圣凡之殊。指其兼气质而发用之心。则容有不同。不同故可以做变化之功。而其本本善。故终复其初也。然而兼气质二字。其义深奥。可精思而不置也。又曰。本然之心。若有不同。则众人虽欲为圣人。所谓乃复其初者。不过复其众人区区之心地。安能至于光明灿烂无一点之累耶。乃复其初之初字。不分圣人众人而为言。则初即明德。明德是本心。本心既有优劣分数。则虽使众人。极其澄治之功。而圣人自圣人。众人自众人。奈何为圣人。又曰。道心是圣凡所同之本心。原于性命者也。人心是圣凡不同之心。而生于形气者也。原于性命之心。是心之本体。而程子所谓心。本善之心。生于形气者。则是气质之心。而朱子所谓气质有蔽之心也。(陶庵明德讲说曰。心之为物。本以妙合理气者而成名。则不可离了这理而独以气字断之也。若必就气上。分析其地头而言之。则气亦有二焉。天地本然之气。纯一不杂者。心之本体也。是所谓明德。此则圣人众人一也。形既生矣。神以发知。是所谓血气之精英。陈安卿以为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者。是也。此则圣人众人。亦自不齐也。此非有两样心。随其地头。而所指各不同。惟在所见之如何耳。)观
之本体。无不仁者也。若以本然之心。为圣人与众人不同。则是明德亦有分数。而程子所谓神一而已者。亦为虚语也。故先师尝曰。兼气质之心则有分数。而其本然之心无分数。明德既无分数。则本心之有分数云者。不成义理。又曰。泛言心而谓之全善则不可。莫如曰。指其本然之心。则固无圣凡之殊。指其兼气质而发用之心。则容有不同。不同故可以做变化之功。而其本本善。故终复其初也。然而兼气质二字。其义深奥。可精思而不置也。又曰。本然之心。若有不同。则众人虽欲为圣人。所谓乃复其初者。不过复其众人区区之心地。安能至于光明灿烂无一点之累耶。乃复其初之初字。不分圣人众人而为言。则初即明德。明德是本心。本心既有优劣分数。则虽使众人。极其澄治之功。而圣人自圣人。众人自众人。奈何为圣人。又曰。道心是圣凡所同之本心。原于性命者也。人心是圣凡不同之心。而生于形气者也。原于性命之心。是心之本体。而程子所谓心。本善之心。生于形气者。则是气质之心。而朱子所谓气质有蔽之心也。(陶庵明德讲说曰。心之为物。本以妙合理气者而成名。则不可离了这理而独以气字断之也。若必就气上。分析其地头而言之。则气亦有二焉。天地本然之气。纯一不杂者。心之本体也。是所谓明德。此则圣人众人一也。形既生矣。神以发知。是所谓血气之精英。陈安卿以为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者。是也。此则圣人众人。亦自不齐也。此非有两样心。随其地头。而所指各不同。惟在所见之如何耳。)观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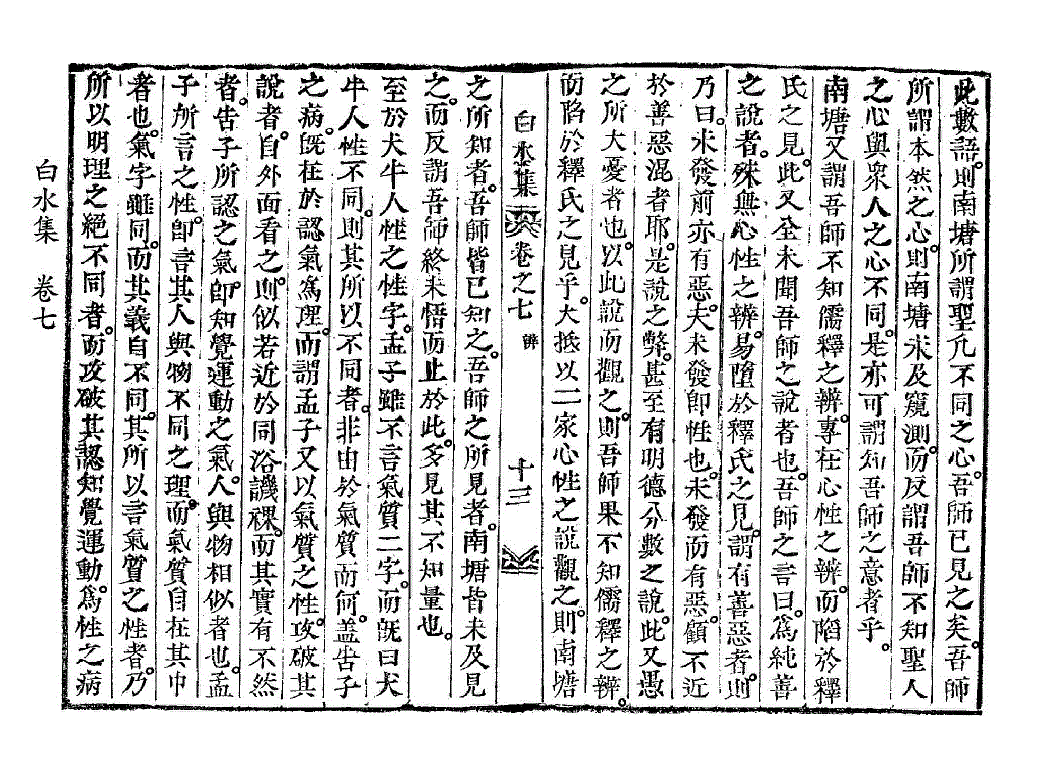 此数语。则南塘所谓圣凡不同之心。吾师已见之矣。吾师所谓本然之心。则南塘未及窥测。而反谓吾师不知圣人之心与众人之心不同。是亦可谓知吾师之意者乎。
此数语。则南塘所谓圣凡不同之心。吾师已见之矣。吾师所谓本然之心。则南塘未及窥测。而反谓吾师不知圣人之心与众人之心不同。是亦可谓知吾师之意者乎。南塘又谓吾师不知儒释之辨。专在心性之辨。而陷于释氏之见。此又全未闻吾师之说者也。吾师之言曰。为纯善之说者。殊无心性之辨。易堕于释氏之见。谓有善恶者。则乃曰。未发前亦有恶。夫未发即性也。未发而有恶。顾不近于善恶混者耶。是说之弊。甚至有明德分数之说。此又愚之所大忧者也。以此说而观之。则吾师果不知儒释之辨。而陷于释氏之见乎。大抵以二家心性之说观之。则南塘之所知者。吾师皆已知之。吾师之所见者。南塘皆未及见之。而反谓吾师终未悟而止于此。多见其不知量也。
至于犬牛人性之性字。孟子虽不言气质二字。而既曰犬牛人性不同。则其所以不同者。非由于气质而何。盖告子之病。既在于认气为理。而谓孟子又以气质之性。攻破其说者。自外面看之。则似若近于同浴讥裸。而其实有不然者。告子所认之气。即知觉运动之气。人与物相似者也。孟子所言之性。即言其人与物不同之理。而气质自在其中者也。气字虽同。而其义自不同。其所以言气质之性者。乃所以明理之绝不同者。而攻破其认知觉运动。为性之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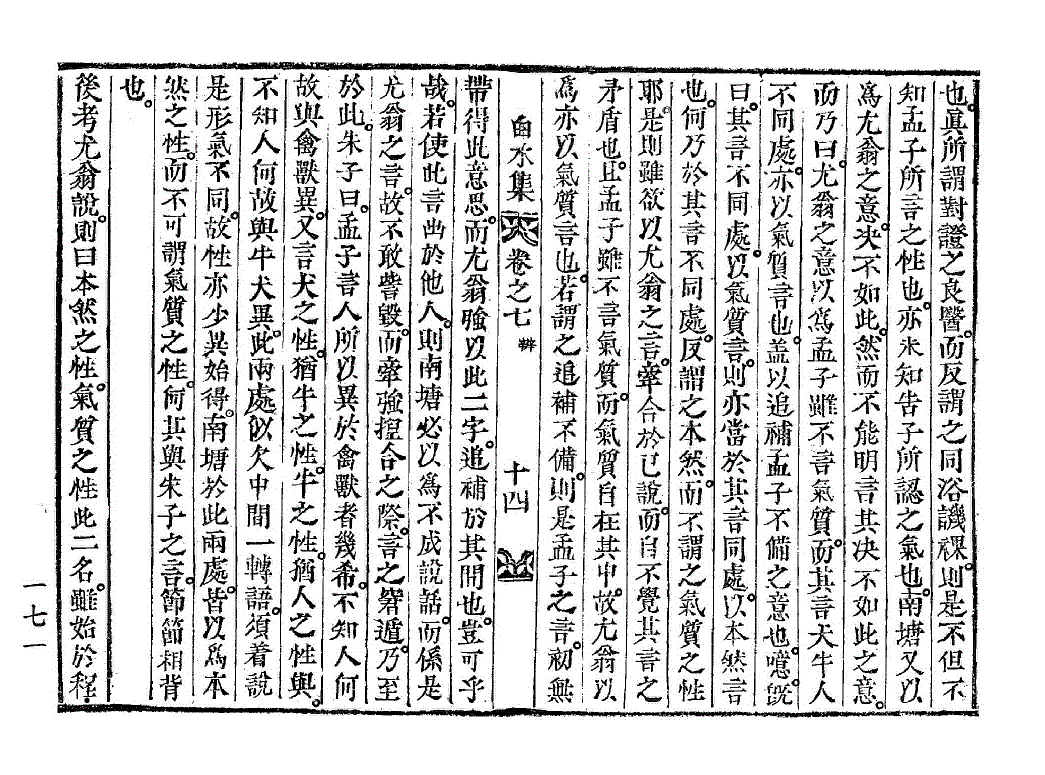 也。真所谓对證之良医。而反谓之同浴讥裸。则是不但不知孟子所言之性也。亦未知告子所认之气也。南塘又以为尤翁之意。决不如此。然而不能明言其决不如此之意。而乃曰。尤翁之意以为孟子虽不言气质。而其言犬牛人不同处。亦以气质言也。盖以追补孟子不备之意也。噫。既曰。其言不同处。以气质言。则亦当于其言同处。以本然言也。何乃于其言不同处。反谓之本然。而不谓之气质之性耶。是则虽欲以尤翁之言。牵合于己说。而自不觉其言之矛盾也。且孟子虽不言气质。而气质自在其中。故尤翁以为亦以气质言也。若谓之追补不备。则是孟子之言。初无带得此意思。而尤翁强以此二字。追补于其间也。岂可乎哉。若使此言出于他人。则南塘必以为不成说话。而系是尤翁之言。故不敢訾毁。而牵强捏合之际。言之窘遁。乃至于此。朱子曰。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南塘于此两处。皆以为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气质之性。何其与朱子之言。节节相背也。
也。真所谓对證之良医。而反谓之同浴讥裸。则是不但不知孟子所言之性也。亦未知告子所认之气也。南塘又以为尤翁之意。决不如此。然而不能明言其决不如此之意。而乃曰。尤翁之意以为孟子虽不言气质。而其言犬牛人不同处。亦以气质言也。盖以追补孟子不备之意也。噫。既曰。其言不同处。以气质言。则亦当于其言同处。以本然言也。何乃于其言不同处。反谓之本然。而不谓之气质之性耶。是则虽欲以尤翁之言。牵合于己说。而自不觉其言之矛盾也。且孟子虽不言气质。而气质自在其中。故尤翁以为亦以气质言也。若谓之追补不备。则是孟子之言。初无带得此意思。而尤翁强以此二字。追补于其间也。岂可乎哉。若使此言出于他人。则南塘必以为不成说话。而系是尤翁之言。故不敢訾毁。而牵强捏合之际。言之窘遁。乃至于此。朱子曰。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异始得。南塘于此两处。皆以为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气质之性。何其与朱子之言。节节相背也。后考尤翁说。则曰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此二名。虽始于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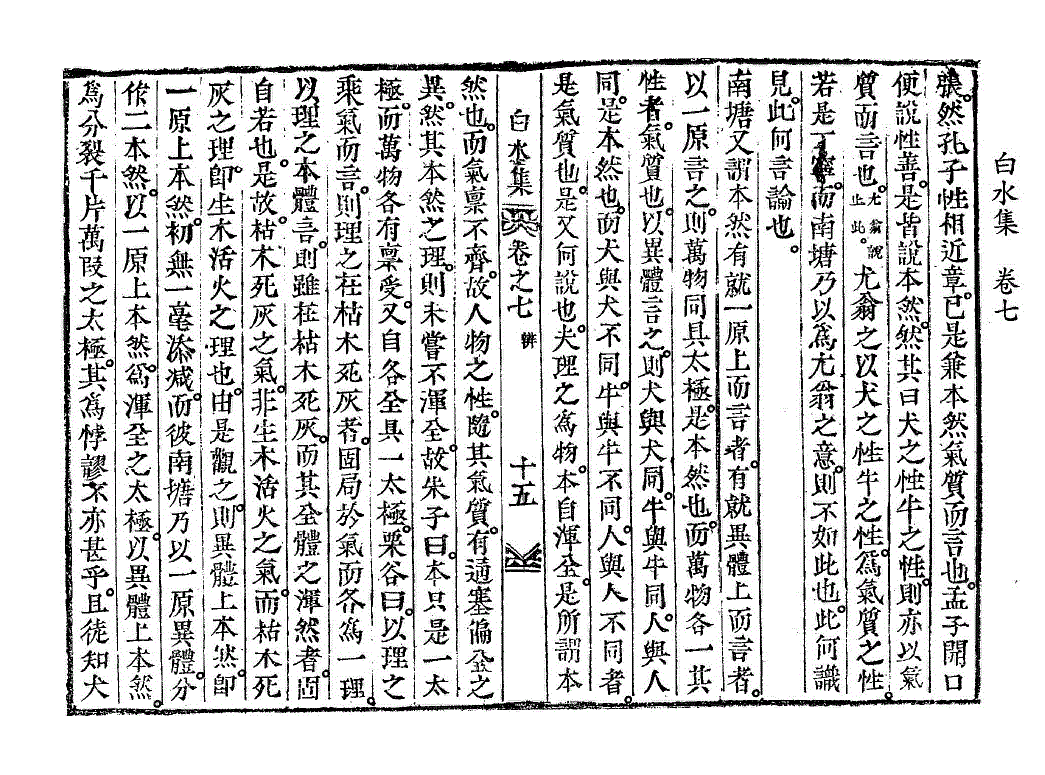 张。然孔子性相近章。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犬之性牛之性。则亦以气质而言也。(尤翁说止此。)尤翁之以犬之性牛之性。为气质之性。若是丁宁。而南塘乃以为尤翁之意。则不如此也。此何识见。此何言论也。
张。然孔子性相近章。已是兼本然气质而言也。孟子开口便说性善。是皆说本然。然其曰犬之性牛之性。则亦以气质而言也。(尤翁说止此。)尤翁之以犬之性牛之性。为气质之性。若是丁宁。而南塘乃以为尤翁之意。则不如此也。此何识见。此何言论也。南塘又谓本然有就一原上而言者。有就异体上而言者。以一原言之。则万物同具太极。是本然也。而万物各一其性者。气质也。以异体言之。则犬与犬同。牛与牛同。人与人同。是本然也。而犬与犬不同。牛与牛不同。人与人不同者。是气质也。是又何说也。夫理之为物。本自浑全。是所谓本然也。而气禀不齐。故人物之性。随其气质。有通塞偏全之异。然其本然之理。则未尝不浑全。故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栗谷曰。以理之乘气而言。则理之在枯木死灰者。固局于气而各为一理。以理之本体言。则虽在枯木死灰。而其全体之浑然者。固自若也。是故。枯木死灰之气。非生木活火之气。而枯木死灰之理。即生木活火之理也。由是观之。则异体上本然。即一原上本然。初无一毫添减。而彼南塘乃以一原异体。分作二本然。以一原上本然。为浑全之太极。以异体上本然。为分裂千片万段之太极。其为悖谬不亦甚乎。且徒知犬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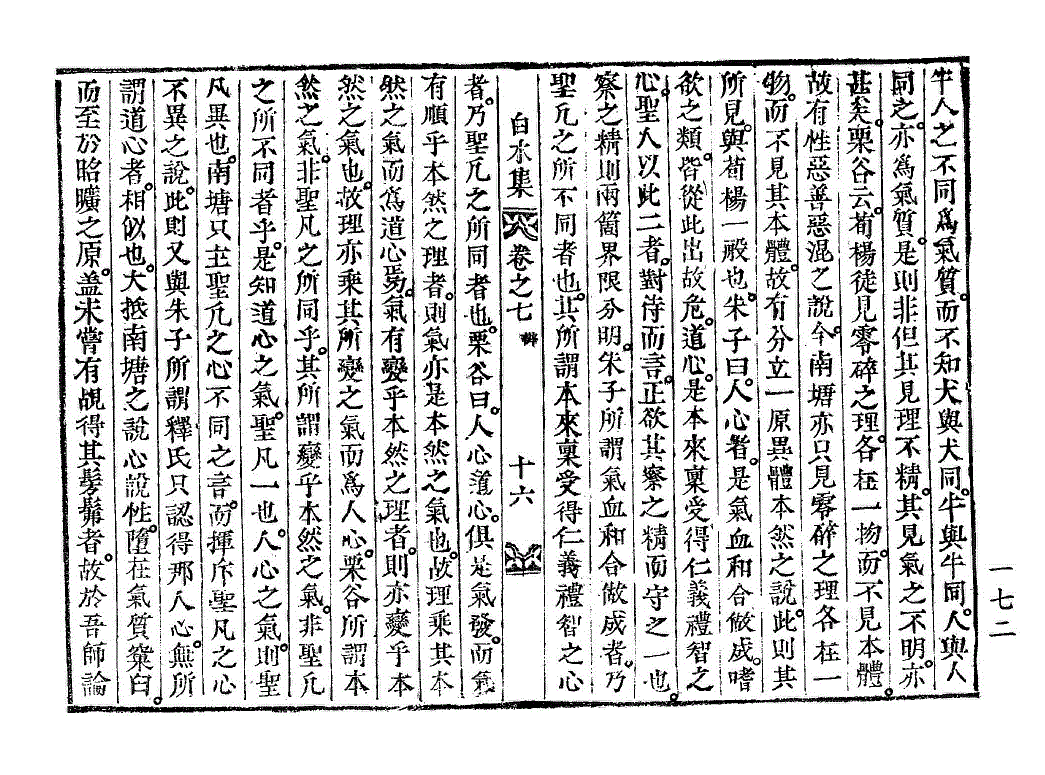 牛人之不同为气质。而不知犬与犬同。牛与牛同。人与人同之。亦为气质。是则非但其见理不精。其见气之不明。亦甚矣。栗谷云。荀杨徒见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见本体。故有性恶善恶混之说。今南塘亦只见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见其本体。故有分立一原异体本然之说。此则其所见。与荀杨一般也。朱子曰。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朱子所谓气血和合做成者。乃圣凡之所不同者也。其所谓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者。乃圣凡之所同者也。栗谷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栗谷所谓本然之气。非圣凡之所同乎。其所谓变乎本然之气。非圣凡之所不同者乎。是知道心之气。圣凡一也。人心之气。则圣凡异也。南塘只主圣凡之心不同之言。而挥斥圣凡之心不异之说。此则又与朱子所谓释氏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者。相似也。大抵南塘之说心说性。堕在气质窠臼。而至于昭旷之原。盖未尝有觇得其髣髴者。故于吾师论
牛人之不同为气质。而不知犬与犬同。牛与牛同。人与人同之。亦为气质。是则非但其见理不精。其见气之不明。亦甚矣。栗谷云。荀杨徒见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见本体。故有性恶善恶混之说。今南塘亦只见零碎之理各在一物。而不见其本体。故有分立一原异体本然之说。此则其所见。与荀杨一般也。朱子曰。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朱子所谓气血和合做成者。乃圣凡之所不同者也。其所谓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者。乃圣凡之所同者也。栗谷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栗谷所谓本然之气。非圣凡之所同乎。其所谓变乎本然之气。非圣凡之所不同者乎。是知道心之气。圣凡一也。人心之气。则圣凡异也。南塘只主圣凡之心不同之言。而挥斥圣凡之心不异之说。此则又与朱子所谓释氏只认得那人心。无所谓道心者。相似也。大抵南塘之说心说性。堕在气质窠臼。而至于昭旷之原。盖未尝有觇得其髣髴者。故于吾师论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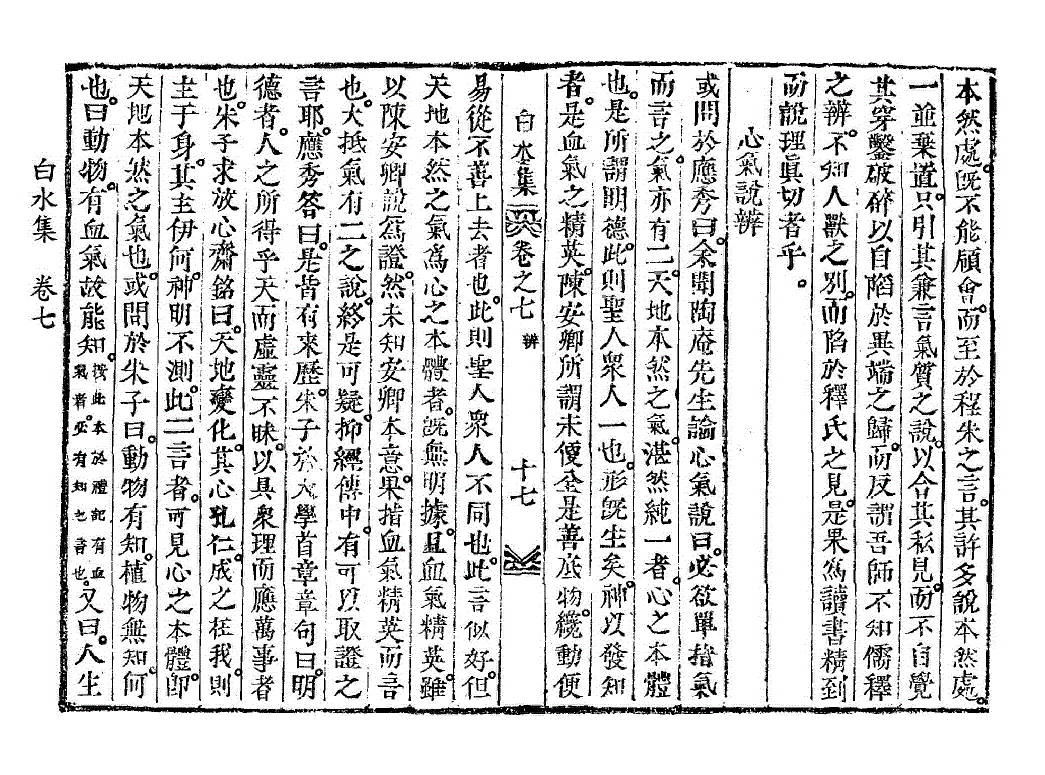 本然处。既不能领会。而至于程朱之言。其许多说本然处。一并弃置。只引其兼言气质之说。以合其私见。而不自觉其穿凿破碎以自陷于异端之归。而反谓吾师不知儒释之辨。不知人兽之别。而陷于释氏之见。是果为读书精到而说理真切者乎。
本然处。既不能领会。而至于程朱之言。其许多说本然处。一并弃置。只引其兼言气质之说。以合其私见。而不自觉其穿凿破碎以自陷于异端之归。而反谓吾师不知儒释之辨。不知人兽之别。而陷于释氏之见。是果为读书精到而说理真切者乎。心气说辨
或问于应秀曰。余闻陶庵先生论心气说曰。必欲单指气而言之。气亦有二。天地本然之气。湛然纯一者。心之本体也。是所谓明德。此则圣人众人一也。形既生矣。神以发知者。是血气之精英。陈安卿所谓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者也。此则圣人众人不同也。此言似好。但天地本然之气为心之本体者。既无明据。且血气精英。虽以陈安卿说为證。然未知安卿本意。果指血气精英而言也。大抵气有二之说。终是可疑。抑经传中。有可以取證之言耶。应秀答曰。是皆有来历。朱子于大学首章章句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子求放心斋铭曰。天地变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则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测。此二言者。可见心之本体。即天地本然之气也。或问于朱子曰。动物有知。植物无知。何也。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按此本于礼记有血气者。必有知之言也。)又曰。人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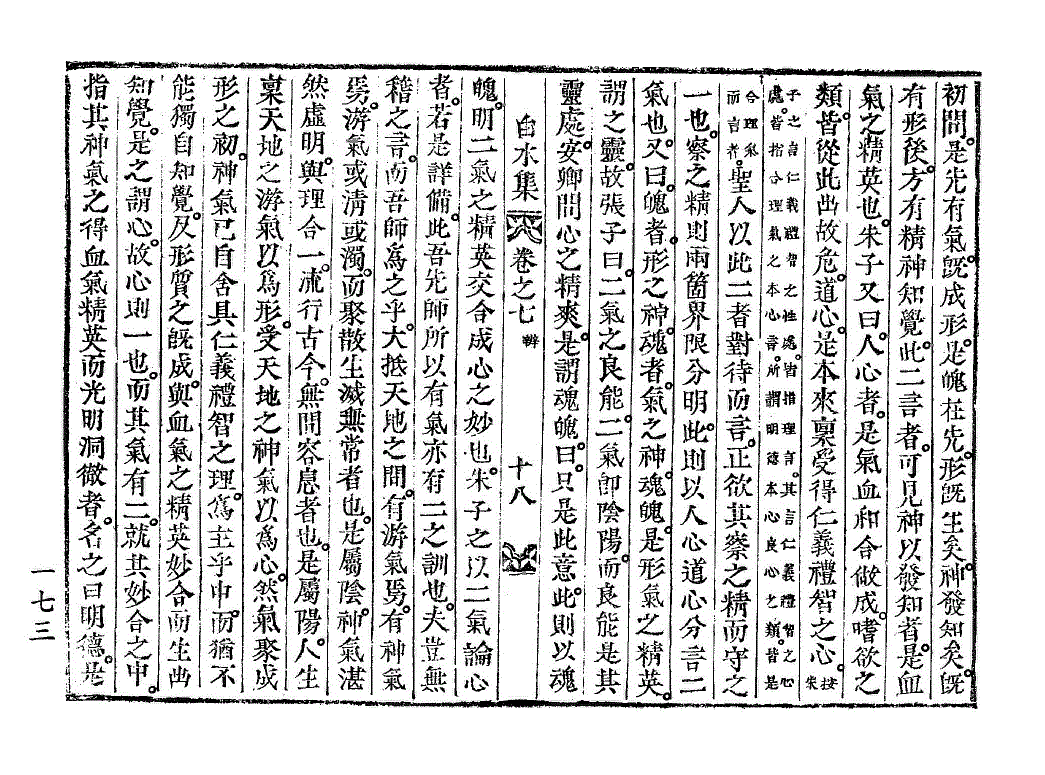 初间。是先有气。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此二言者。可见神以发知者。是血气之精英也。朱子又曰。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按朱子之言仁义礼智之性处。皆指理言。其言仁义礼智之心处。皆指合理气之本心言。所谓明德本心良心之类。皆是合理气而言者。)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此则以人心道心分言二气也。又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魂魄。是形气之精英。谓之灵。故张子曰。二气之良能。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安卿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曰。只是此意。此则以魂魄。明二气之精英交合成心之妙也。朱子之以二气论心者。若是详备。此吾先师所以有气亦有二之训也。夫岂无稽之言。而吾师为之乎。大抵天地之间。有游气焉。有神气焉。游气或清或浊。而聚散生灭无常者也。是属阴。神气湛然虚明。与理合一。流行古今。无间容息者也。是属阳。人生禀天地之游气以为形。受天地之神气以为心。然气聚成形之初。神气已自含具仁义礼智之理。为主乎中。而犹不能独自知觉。及形质之既成。与血气之精英妙合而生出知觉。是之谓心。故心则一也。而其气有二。就其妙合之中。指其神气之得血气精英而光明洞彻者。名之曰明德。是
初间。是先有气。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此二言者。可见神以发知者。是血气之精英也。朱子又曰。人心者。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按朱子之言仁义礼智之性处。皆指理言。其言仁义礼智之心处。皆指合理气之本心言。所谓明德本心良心之类。皆是合理气而言者。)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此则以人心道心分言二气也。又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魂魄。是形气之精英。谓之灵。故张子曰。二气之良能。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安卿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曰。只是此意。此则以魂魄。明二气之精英交合成心之妙也。朱子之以二气论心者。若是详备。此吾先师所以有气亦有二之训也。夫岂无稽之言。而吾师为之乎。大抵天地之间。有游气焉。有神气焉。游气或清或浊。而聚散生灭无常者也。是属阴。神气湛然虚明。与理合一。流行古今。无间容息者也。是属阳。人生禀天地之游气以为形。受天地之神气以为心。然气聚成形之初。神气已自含具仁义礼智之理。为主乎中。而犹不能独自知觉。及形质之既成。与血气之精英妙合而生出知觉。是之谓心。故心则一也。而其气有二。就其妙合之中。指其神气之得血气精英而光明洞彻者。名之曰明德。是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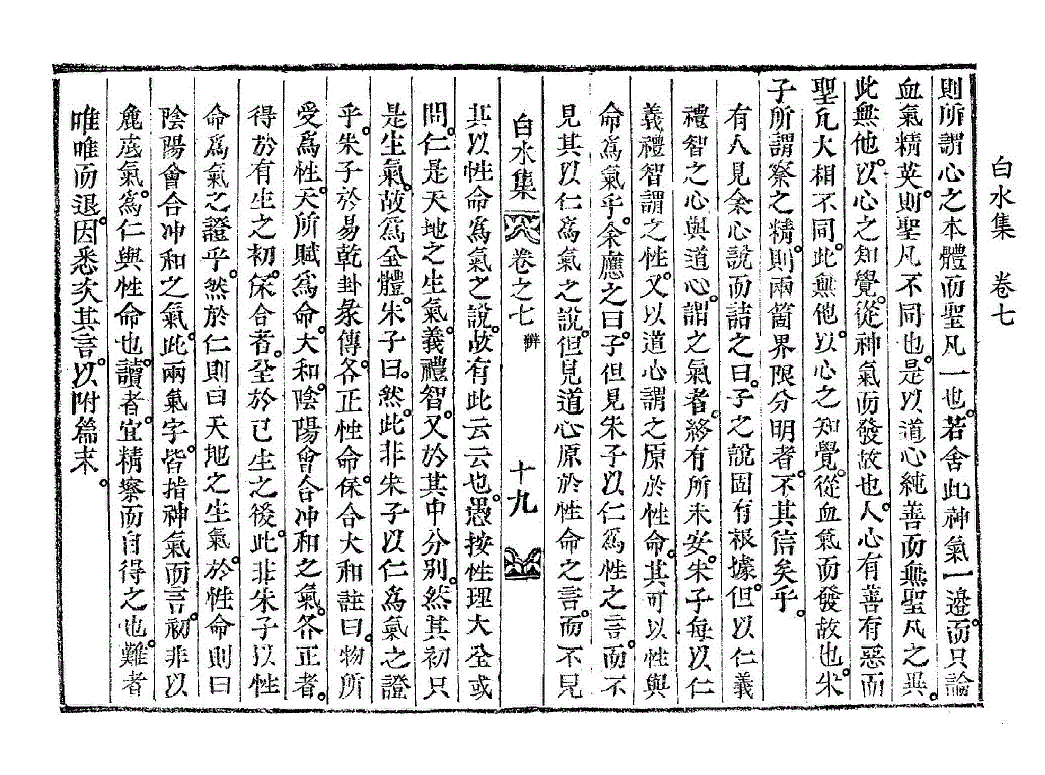 则所谓心之本体而圣凡一也。若舍此神气一边。而只论血气精英。则圣凡不同也。是以道心纯善而无圣凡之异。此无他。以心之知觉。从神气而发故也。人心有善有恶而圣凡大相不同。此无他。以心之知觉。从血气而发故也。朱子所谓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者。不其信矣乎。
则所谓心之本体而圣凡一也。若舍此神气一边。而只论血气精英。则圣凡不同也。是以道心纯善而无圣凡之异。此无他。以心之知觉。从神气而发故也。人心有善有恶而圣凡大相不同。此无他。以心之知觉。从血气而发故也。朱子所谓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者。不其信矣乎。有人见余心说而诘之曰。子之说固有根据。但以仁义礼智之心与道心。谓之气者。终有所未安。朱子每以仁义礼智谓之性。又以道心谓之原于性命。其可以性与命为气乎。余应之曰。子但见朱子以仁为性之言。而不见其以仁为气之说。但见道心原于性命之言。而不见其以性命为气之说。故有此云云也。愚按性理大全或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朱子曰。然。此非朱子以仁为气之證乎。朱子于易乾卦彖传。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注曰。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非朱子以性命为气之證乎。然于仁则曰天地之生气。于性命则曰阴阳会合冲和之气。此两气字。皆指神气而言。初非以粗底气。为仁与性命也。读者。宜精察而自得之也。难者唯唯而退。因悉次其言。以附篇末。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4L 页
 或曰。闻子之言。则心之有二气。果有明据。然心既有二气。则朱子之论心。何不以合二气者言之。而或只言本然。或只言血气。何也。曰。此则所指之地头各异。故随其地头而言。自不得不然。如大学之明德。亦非离乎。血气者。但其所指地头。乃指心之至精至妙。粹然无杂之体而言者。则于此虽欲言血气。其可得乎。此朱子所以专以本然之气释之者也。至于知觉。则是本然与血气交合而后生者。非血气独能知觉也。但植物之所以无知。动物之所以有知。则实由于血气之有无。故朱子于或人之问。则专以血气言之。而于人心道心。则以二气分言之。于心之精爽虚灵知觉处。则以二气合言之。此朱子之言。所以曲畅旁通。无不恰好也。或曰。然则有血气者之所以有知。无血气者之所以无知。何也。曰。夫天地之理。二气交合。然后能化生万物。知觉之所由生。其理亦然。本然属阳。血气属阴。阴阳交合而生知觉焉。若无血气。则独阳安能变化乎。此动物之所以有知而植物之所以无知也。子如不信愚言。且去细看朱子书。或曰。有血气者有知。无血气者无知之理。则既闻命矣。敢问植物之所以无血气。动物之所以有血气者。何。曰。此则未闻先贤之说。然礼记有天产地产之语。意者动物天产。禀得阳气多。故有血气而煖。植物地产。禀得阴气
或曰。闻子之言。则心之有二气。果有明据。然心既有二气。则朱子之论心。何不以合二气者言之。而或只言本然。或只言血气。何也。曰。此则所指之地头各异。故随其地头而言。自不得不然。如大学之明德。亦非离乎。血气者。但其所指地头。乃指心之至精至妙。粹然无杂之体而言者。则于此虽欲言血气。其可得乎。此朱子所以专以本然之气释之者也。至于知觉。则是本然与血气交合而后生者。非血气独能知觉也。但植物之所以无知。动物之所以有知。则实由于血气之有无。故朱子于或人之问。则专以血气言之。而于人心道心。则以二气分言之。于心之精爽虚灵知觉处。则以二气合言之。此朱子之言。所以曲畅旁通。无不恰好也。或曰。然则有血气者之所以有知。无血气者之所以无知。何也。曰。夫天地之理。二气交合。然后能化生万物。知觉之所由生。其理亦然。本然属阳。血气属阴。阴阳交合而生知觉焉。若无血气。则独阳安能变化乎。此动物之所以有知而植物之所以无知也。子如不信愚言。且去细看朱子书。或曰。有血气者有知。无血气者无知之理。则既闻命矣。敢问植物之所以无血气。动物之所以有血气者。何。曰。此则未闻先贤之说。然礼记有天产地产之语。意者动物天产。禀得阳气多。故有血气而煖。植物地产。禀得阴气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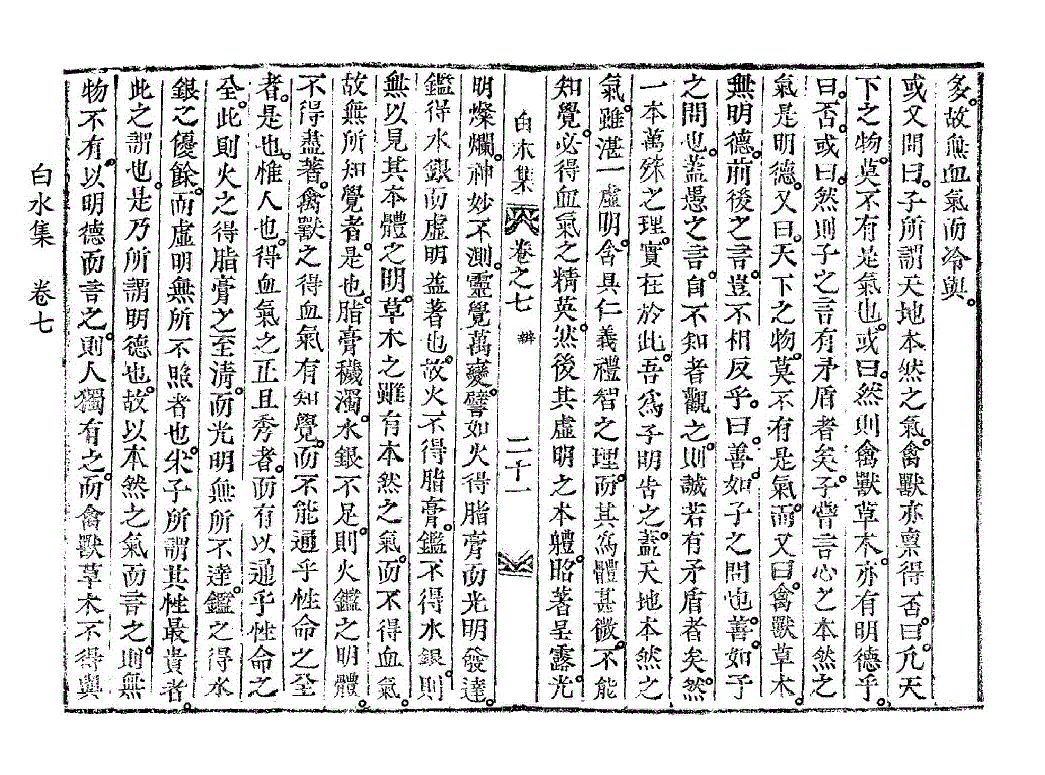 多。故无血气而冷与。
多。故无血气而冷与。或又问曰。子所谓天地本然之气。禽兽亦禀得否。曰。凡天下之物。莫不有是气也。或曰。然则禽兽草木。亦有明德乎。曰。否。或曰。然则子之言有矛盾者矣。子尝言心之本然之气是明德。又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是气。而又曰。禽兽草木。无明德。前后之言。岂不相反乎。曰。善。如子之问也。善。如子之问也。盖愚之言。自不知者观之。则诚若有矛盾者矣。然一本万殊之理。实在于此。吾为子明告之。盖天地本然之气。虽湛一虚明。含具仁义礼智之理。而其为体甚微。不能知觉。必得血气之精英。然后其虚明之本体。昭著呈露。光明灿烂。神妙不测。灵觉万变。譬如火得脂膏而光明发达。鉴得水银而虚明益著也。故火不得脂膏。鉴不得水银。则无以见其本体之明。草木之虽有本然之气。而不得血气。故无所知觉者。是也。脂膏秽浊。水银不足。则火鉴之明体。不得尽著。禽兽之得血气有知觉。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者。是也。惟人也。得血气之正且秀者。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此则火之得脂膏之至清。而光明无所不达。鉴之得水银之优馀。而虚明无所不照者也。朱子所谓其性最贵者。此之谓也。是乃所谓明德也。故以本然之气而言之。则无物不有。以明德而言之。则人独有之。而禽兽草木不得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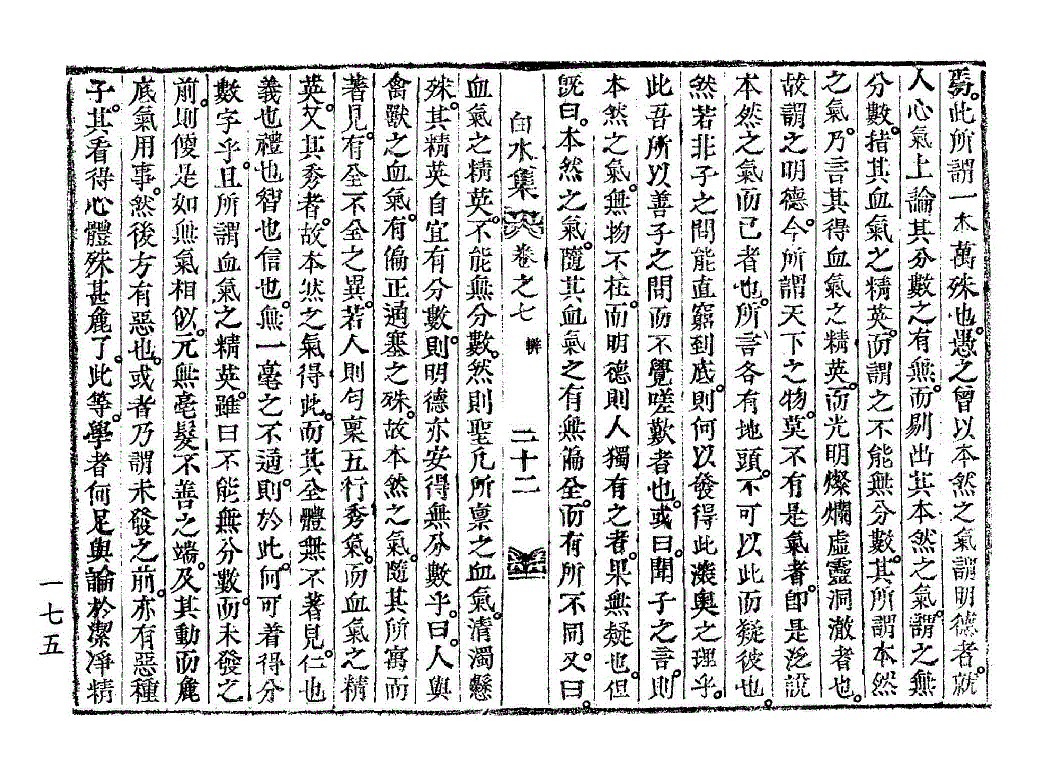 焉。此所谓一本万殊也。愚之曾以本然之气谓明德者。就人心气上论其分数之有无。而剔出其本然之气。谓之无分数。指其血气之精英。而谓之不能无分数。其所谓本然之气。乃言其得血气之精英。而光明灿烂虚灵洞澈者也。故谓之明德。今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是气者。即是泛说本然之气而已者也。所言各有地头。不可以此而疑彼也。然若非子之问能直穷到底。则何以发得此深奥之理乎。此吾所以善子之问而不觉嗟叹者也。或曰。闻子之言。则本然之气。无物不在。而明德则人独有之者。果无疑也。但既曰。本然之气。随其血气之有无偏全。而有所不同。又曰。血气之精英。不能无分数。然则圣凡所禀之血气。清浊悬殊。其精英自宜有分数。则明德亦安得无分数乎。曰。人与禽兽之血气。有偏正通塞之殊。故本然之气。随其所寓而著见。有全不全之异。若人则匀禀五行秀气。而血气之精英。又其秀者。故本然之气得此。而其全体无不著见。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无一毫之不通。则于此。何可着得分数字乎。且所谓血气之精英。虽曰不能无分数。而未发之前。则便是如无气相似。元无毫发不善之端。及其动而粗底气用事。然后方有恶也。或者乃谓未发之前。亦有恶种子。其看得心体殊甚粗了。此等。学者何足与论于洁净精
焉。此所谓一本万殊也。愚之曾以本然之气谓明德者。就人心气上论其分数之有无。而剔出其本然之气。谓之无分数。指其血气之精英。而谓之不能无分数。其所谓本然之气。乃言其得血气之精英。而光明灿烂虚灵洞澈者也。故谓之明德。今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是气者。即是泛说本然之气而已者也。所言各有地头。不可以此而疑彼也。然若非子之问能直穷到底。则何以发得此深奥之理乎。此吾所以善子之问而不觉嗟叹者也。或曰。闻子之言。则本然之气。无物不在。而明德则人独有之者。果无疑也。但既曰。本然之气。随其血气之有无偏全。而有所不同。又曰。血气之精英。不能无分数。然则圣凡所禀之血气。清浊悬殊。其精英自宜有分数。则明德亦安得无分数乎。曰。人与禽兽之血气。有偏正通塞之殊。故本然之气。随其所寓而著见。有全不全之异。若人则匀禀五行秀气。而血气之精英。又其秀者。故本然之气得此。而其全体无不著见。仁也义也礼也智也信也。无一毫之不通。则于此。何可着得分数字乎。且所谓血气之精英。虽曰不能无分数。而未发之前。则便是如无气相似。元无毫发不善之端。及其动而粗底气用事。然后方有恶也。或者乃谓未发之前。亦有恶种子。其看得心体殊甚粗了。此等。学者何足与论于洁净精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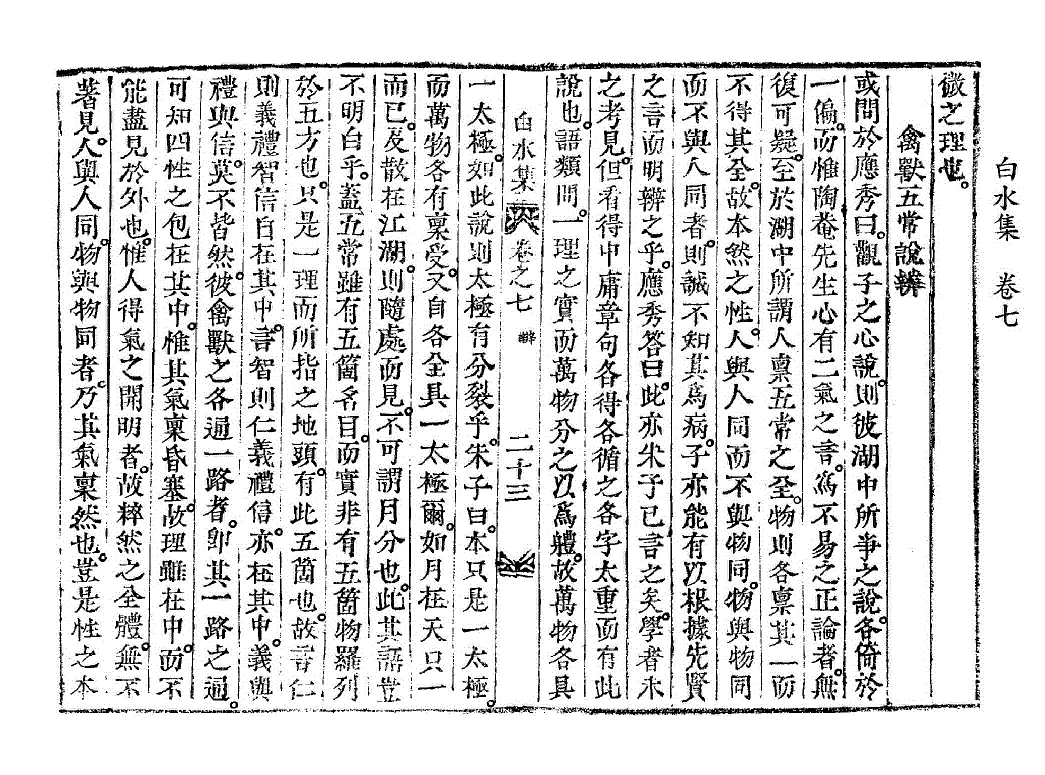 微之理也。
微之理也。禽兽五常说辨
或问于应秀曰。观子之心说。则彼湖中所争之说。各倚于一偏。而惟陶庵先生心有二气之言。为不易之正论者。无复可疑。至于湖中所谓人禀五常之全。物则各禀其一而不得其全。故本然之性。人与人同而不与物同。物与物同而不与人同者。则诚不知其为病。子亦能有以根据先贤之言而明辨之乎。应秀答曰。此亦朱子已言之矣。学者未之考见。但看得中庸章句各得各循之各字太重而有此说也。语类问。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各具一太极。如此说则太极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分也。此其语岂不明白乎。盖五常虽有五个名目。而实非有五个物罗列于五方也。只是一理而所指之地头。有此五个也。故言仁则义礼智信自在其中。言智则仁义礼信。亦在其中。义与礼与信。莫不皆然。彼禽兽之各通一路者。即其一路之通。可知四性之包在其中。惟其气禀昏塞。故理虽在中。而不能尽见于外也。惟人得气之开明者。故粹然之全体。无不著见。人与人同。物与物同者。乃其气禀然也。岂是性之本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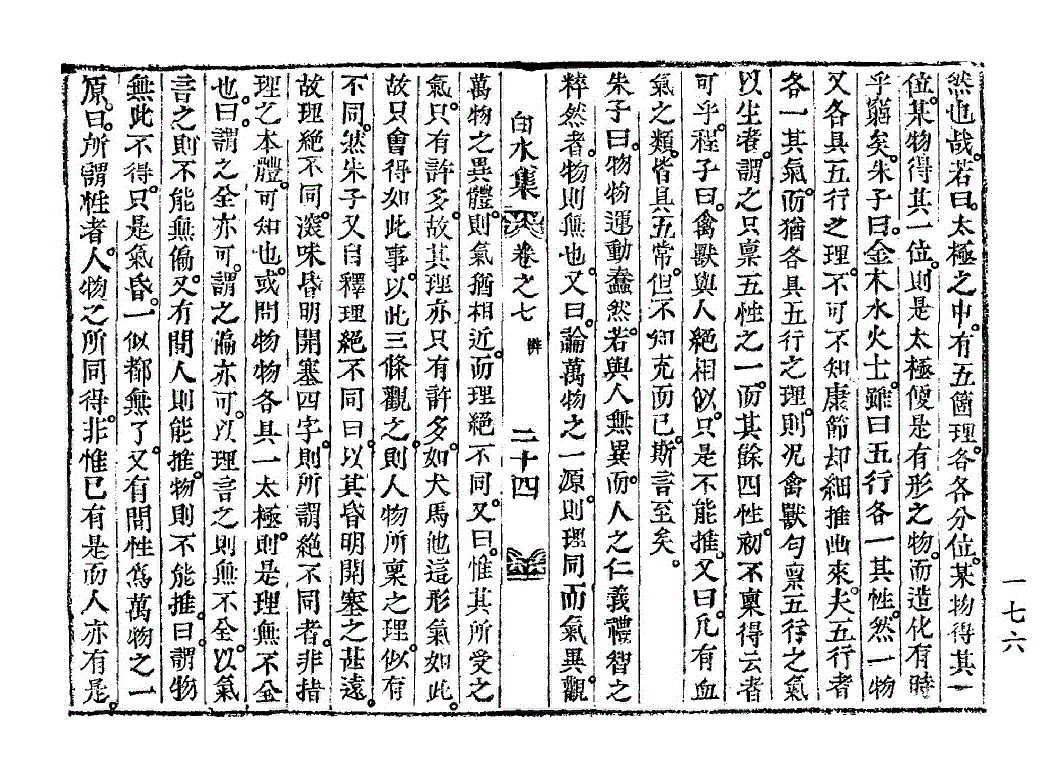 然也哉。若曰。太极之中。有五个理。各各分位。某物得其一位。某物得其一位。则是太极便是有形之物。而造化有时乎穷矣。朱子曰。金木水火土。虽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节却细推出来。夫五行者各一其气。而犹各具五行之理。则况禽兽匀禀五行之气以生者。谓之只禀五性之一。而其馀四性。初不禀得云者可乎。程子曰。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又曰。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斯言至矣。
然也哉。若曰。太极之中。有五个理。各各分位。某物得其一位。某物得其一位。则是太极便是有形之物。而造化有时乎穷矣。朱子曰。金木水火土。虽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节却细推出来。夫五行者各一其气。而犹各具五行之理。则况禽兽匀禀五行之气以生者。谓之只禀五性之一。而其馀四性。初不禀得云者可乎。程子曰。禽兽与人绝相似。只是不能推。又曰。凡有血气之类。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斯言至矣。朱子曰。物物运动蠢然。若与人无异。而人之仁义礼智之粹然者。物则无也。又曰。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又曰。惟其所受之气。只有许多。故其理亦只有许多。如犬马他这形气如此。故只会得如此事。以此三条观之。则人物所禀之理。似有不同。然朱子又自释理绝不同曰。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深味昏明开塞四字。则所谓绝不同者。非指理之本体。可知也。或问物物各具一太极。则是理无不全也。曰。谓之全亦可。谓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又有问人则能推。物则不能推。曰。谓物无此不得。只是气昏。一似都无了。又有问性为万物之一原。曰。所谓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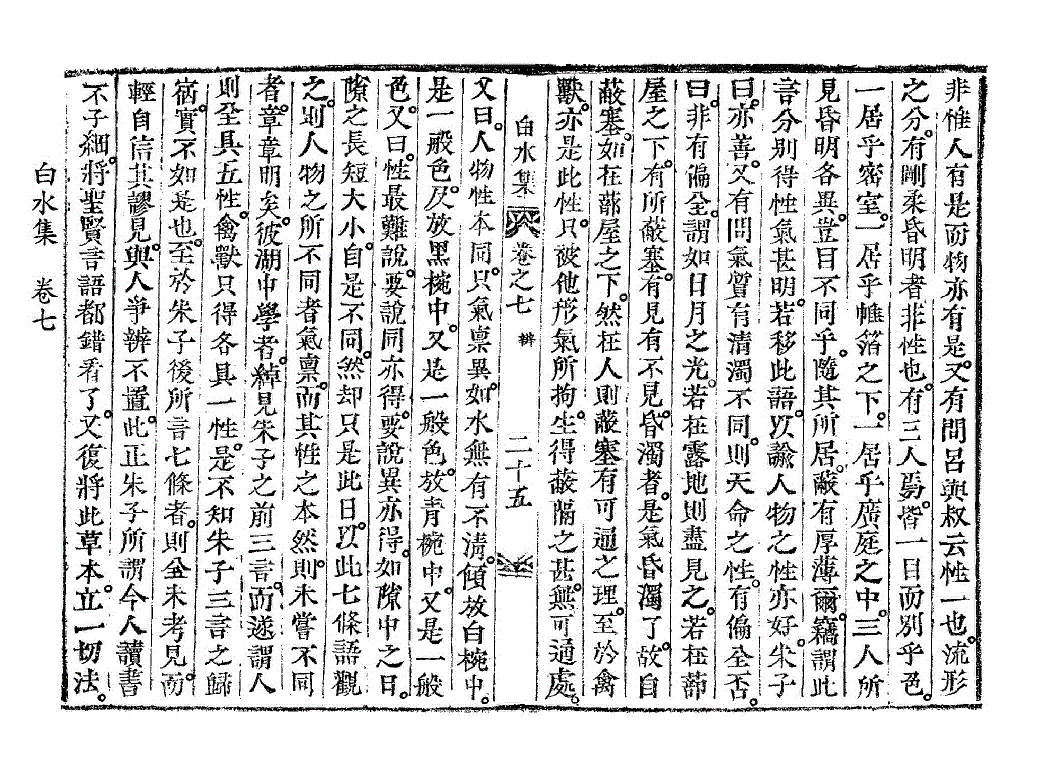 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又有问吕与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刚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别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广庭之中。三人所见昏明各异。岂目不同乎。随其所居。蔽有厚薄尔。窃谓此言分别得性气甚明。若移此语。以谕人物之性亦好。朱子曰。亦善。又有问气质有清浊不同。则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见有不见。昏浊者。是气昏浊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又曰。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如水无有不清。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长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以此七条语观之。则人物之所不同者气禀。而其性之本然。则未尝不同者。章章明矣。彼湖中学者。绰见朱子之前三言。而遂谓人则全具五性。禽兽只得各具一性。是不知朱子三言之归宿。实不如是也。至于朱子后所言七条者。则全未考见。而轻自信其谬见。与人争辨不置。此正朱子所谓今人读书不子细。将圣贤言语都错看了。又复将此草本。立一切法。
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又有问吕与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刚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别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广庭之中。三人所见昏明各异。岂目不同乎。随其所居。蔽有厚薄尔。窃谓此言分别得性气甚明。若移此语。以谕人物之性亦好。朱子曰。亦善。又有问气质有清浊不同。则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见有不见。昏浊者。是气昏浊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又曰。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如水无有不清。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难说。要说同亦得。要说异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长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以此七条语观之。则人物之所不同者气禀。而其性之本然。则未尝不同者。章章明矣。彼湖中学者。绰见朱子之前三言。而遂谓人则全具五性。禽兽只得各具一性。是不知朱子三言之归宿。实不如是也。至于朱子后所言七条者。则全未考见。而轻自信其谬见。与人争辨不置。此正朱子所谓今人读书不子细。将圣贤言语都错看了。又复将此草本。立一切法。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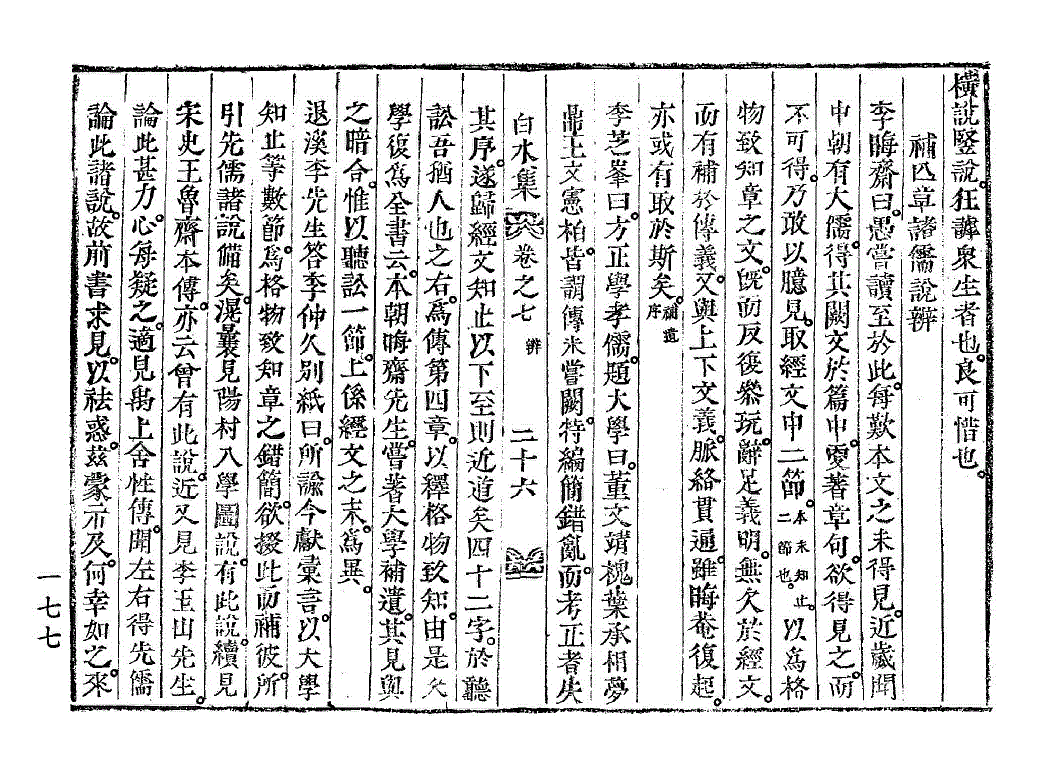 横说竖说。狂謼众生者也。良可惜也。
横说竖说。狂謼众生者也。良可惜也。补亡章诸儒说辨
李晦斋曰。愚尝读至于此。每叹本文之未得见。近岁闻中朝有大儒。得其阙文于篇中。更著章句。欲得见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见。取经文中二节。(本末知止。二节也。)以为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复参玩。辞足义明。无欠于经文。而有补于传义。又与上下文义。脉络贯通。虽晦庵复起。亦或有取于斯矣。(补遗序)
李芝峰曰。方正学孝儒。题大学曰。董文靖槐,叶承相梦鼎,王文宪柏。昔谓传未尝阙。特编简错乱。而考正者失其序。遂归经文知止以下至则近道矣四十二字。于听讼吾犹人也之右。为传第四章。以释格物致知。由是大学复为全书云。本朝晦斋先生。尝著大学补遗。其见与之暗合。惟以听讼一节。上系经文之末。为异。
退溪李先生答李仲久别纸曰。所谕今献汇言。以大学知止等数节。为格物致知章之错简。欲掇此而补彼。所引先儒诸说备矣。滉曩见阳村入学图说。有此说。续见宋史王鲁斋本传。亦云曾有此说。近又见李玉山先生。论此甚力。心每疑之。适见禹上舍性传。闻左右得先儒论此诸说。故前书求见。以祛惑。玆蒙示及。何幸如之。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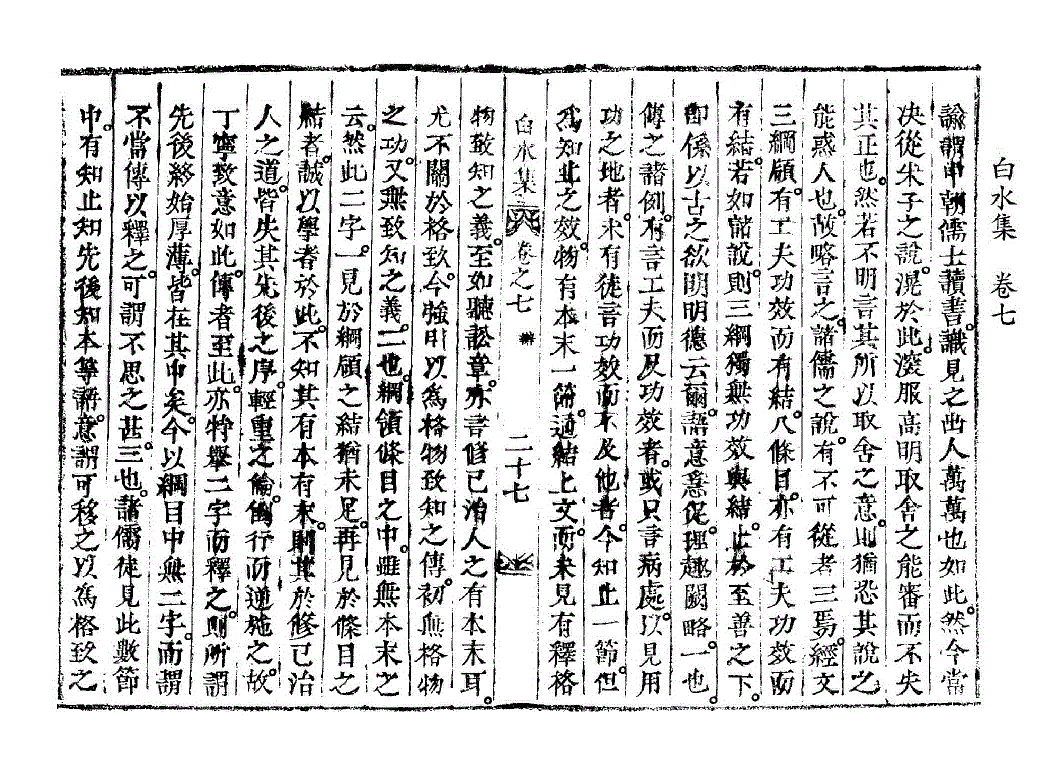 谕谓中朝儒士读书。识见之出人万万也如此。然今当决从朱子之说。滉于此。深服高明取舍之能审而不失其正也。然若不明言其所以取舍之意。则犹恐其说之能惑人也。故略言之。诸儒之说。有不可从者三焉。经文三纲领。有工夫功效而有结。八条目。亦有工夫功效而有结。若如诸说。则三纲独无功效与结。止于至善之下。即系以古之欲明明德云尔。语意急促。理趣阙略。一也。传之诸例。有言工夫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处。以见用功之地者。未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节。但为知止之效。物有本末一节。通结上文。而未见有释格物致知之义。至如听讼章。亦言修己治人之有本末耳。尤不关于格致。今强引以为格物致知之传。初无格物之功。又无致知之义。二也。纲领条目之中。虽无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见于纲领之结犹未足。再见于条目之结者。诚以学者于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则其于修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宁致意如此。传者至此。亦特举二字而释之。则所谓先后终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纲目中无二字。而谓不当传以释之。可谓不思之甚。三也。诸儒徒见此数节中。有知止知先后知本等语。意谓可移之以为格致之
谕谓中朝儒士读书。识见之出人万万也如此。然今当决从朱子之说。滉于此。深服高明取舍之能审而不失其正也。然若不明言其所以取舍之意。则犹恐其说之能惑人也。故略言之。诸儒之说。有不可从者三焉。经文三纲领。有工夫功效而有结。八条目。亦有工夫功效而有结。若如诸说。则三纲独无功效与结。止于至善之下。即系以古之欲明明德云尔。语意急促。理趣阙略。一也。传之诸例。有言工夫而及功效者。或只言病处。以见用功之地者。未有徒言功效而不及他者。今知止一节。但为知止之效。物有本末一节。通结上文。而未见有释格物致知之义。至如听讼章。亦言修己治人之有本末耳。尤不关于格致。今强引以为格物致知之传。初无格物之功。又无致知之义。二也。纲领条目之中。虽无本末之云。然此二字。一见于纲领之结犹未足。再见于条目之结者。诚以学者于此。不知其有本有末。则其于修己治人之道。皆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倒行而逆施之。故丁宁致意如此。传者至此。亦特举二字而释之。则所谓先后终始厚薄。皆在其中矣。今以纲目中无二字。而谓不当传以释之。可谓不思之甚。三也。诸儒徒见此数节中。有知止知先后知本等语。意谓可移之以为格致之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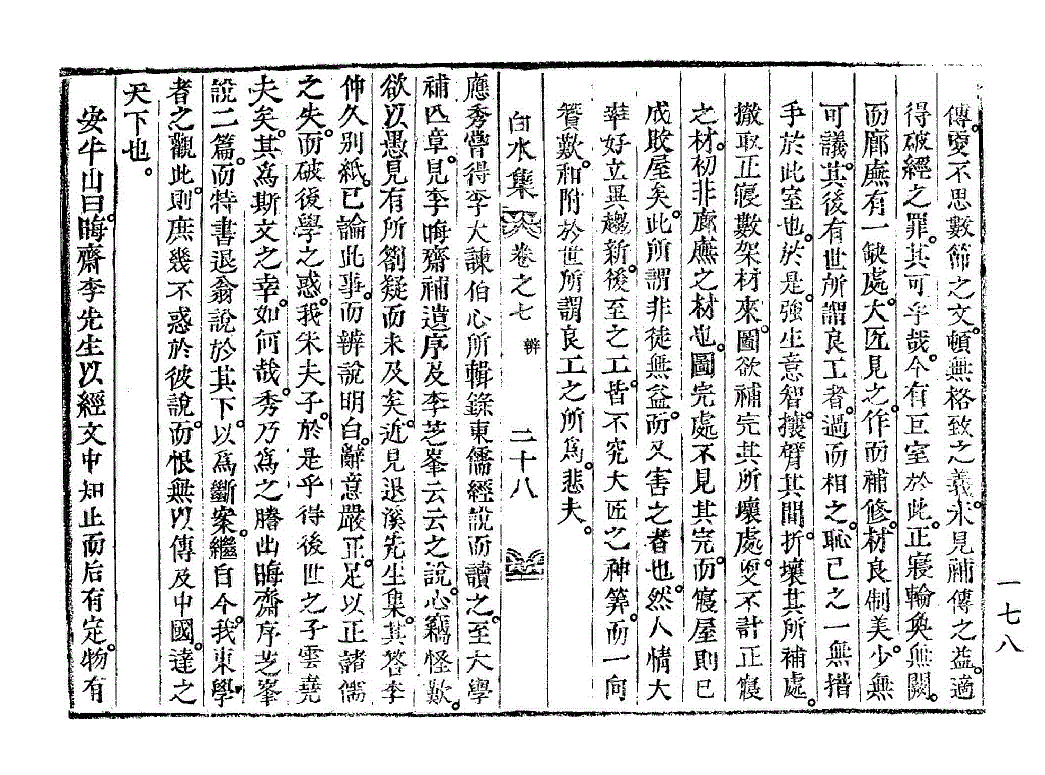 传。更不思数节之文。顿无格致之义。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于此。正寝轮奂无阙。而廊庑有一缺处。大匠见之。作而补修。材良制美。少无可议。其后有世所谓良工者。过而相之。耻己之一无措手于此室也。于是。强生意智。攘臂其间。折坏其所补处。撤取正寝数架材来。图欲补完其所坏处。更不计正寝之材。初非廊庑之材也。图完处不见其完。而寝屋则已成败屋矣。此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大率好立异趋新。后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算。而一向赞叹。和附于世所谓良工之所为。悲夫。
传。更不思数节之文。顿无格致之义。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其可乎哉。今有巨室于此。正寝轮奂无阙。而廊庑有一缺处。大匠见之。作而补修。材良制美。少无可议。其后有世所谓良工者。过而相之。耻己之一无措手于此室也。于是。强生意智。攘臂其间。折坏其所补处。撤取正寝数架材来。图欲补完其所坏处。更不计正寝之材。初非廊庑之材也。图完处不见其完。而寝屋则已成败屋矣。此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然人情大率好立异趋新。后至之工。皆不究大匠之神算。而一向赞叹。和附于世所谓良工之所为。悲夫。应秀尝得李大谏伯心所辑录东儒经说而读之。至大学补亡章。见李晦斋补遗序及李芝峰云云之说。心窃怪叹。欲以愚见有所劄疑而未及矣。近见退溪先生集。其答李仲久别纸。已论此事。而辨说明白。辞意严正。足以正诸儒之失。而破后学之惑。我朱夫子。于是乎得后世之子云尧夫矣。其为斯文之幸。如何哉。秀乃为之誊出晦斋序芝峰说二篇。而特书退翁说于其下。以为断案。继自今。我东学者之观此。则庶几不惑于彼说。而恨无以传及中国。达之天下也。
安牛山曰。晦斋李先生以经文中知止而后有定。物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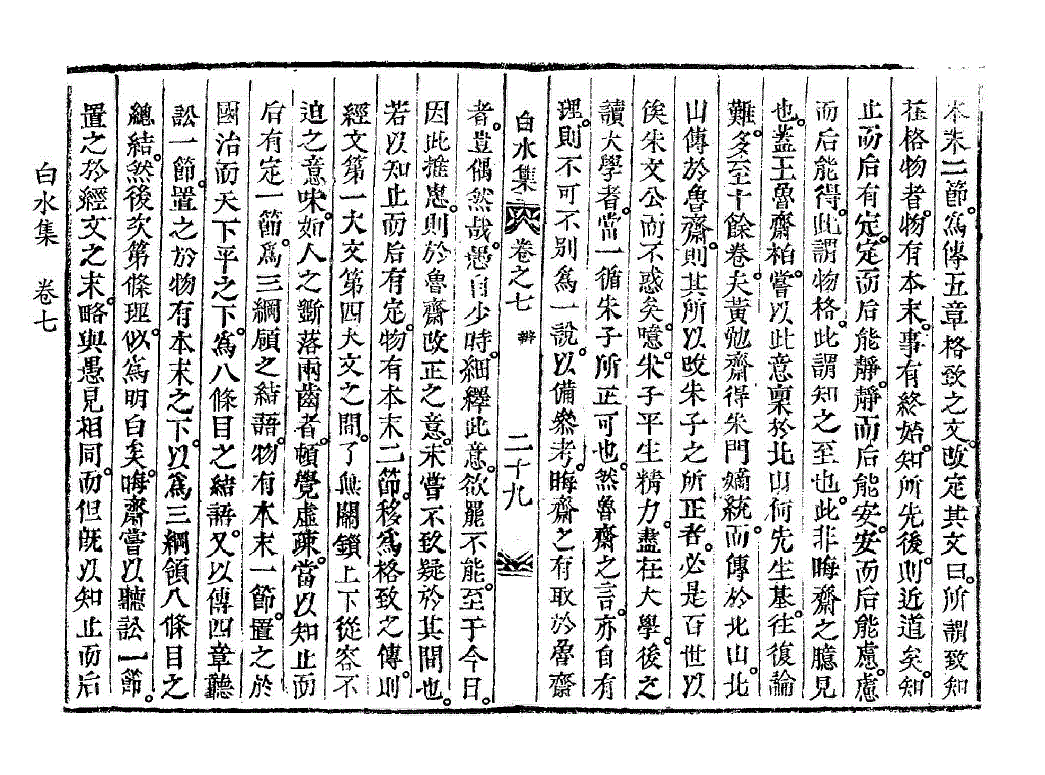 本末二节。为传五章格致之文。改定其文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此非晦斋之臆见也。盖王鲁斋柏。尝以此意禀于北山何先生基。往复论难。多至十馀卷。夫黄勉斋得朱门嫡统。而传于北山。北山传于鲁斋。则其所以改朱子之所正者。必是百世以俟朱文公而不惑矣。噫。朱子平生精力。尽在大学。后之读大学者。当一循朱子所正可也。然鲁斋之言。亦自有理。则不可不别为一说。以备参考。晦斋之有取于鲁斋者。岂偶然哉。愚自少时。细绎此意。欲罢不能。至于今日。因此推思。则于鲁斋改正之意。未尝不致疑于其间也。若以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二节。移为格致之传。则经文第一大文第四大文之间。了无关锁上下从容不迫之意味。如人之斲落两齿者。顿觉虚疏。当以知止而后有定一节。为三纲领之结语。物有本末一节。置之于国治而天下平之下。为八条目之结语。又以传四章听讼一节。置之于物有本末之下。以为三纲领八条目之总结。然后次第条理。似为明白矣。晦斋尝以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略与愚见相同。而但既以知止而后
本末二节。为传五章格致之文。改定其文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此非晦斋之臆见也。盖王鲁斋柏。尝以此意禀于北山何先生基。往复论难。多至十馀卷。夫黄勉斋得朱门嫡统。而传于北山。北山传于鲁斋。则其所以改朱子之所正者。必是百世以俟朱文公而不惑矣。噫。朱子平生精力。尽在大学。后之读大学者。当一循朱子所正可也。然鲁斋之言。亦自有理。则不可不别为一说。以备参考。晦斋之有取于鲁斋者。岂偶然哉。愚自少时。细绎此意。欲罢不能。至于今日。因此推思。则于鲁斋改正之意。未尝不致疑于其间也。若以知止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二节。移为格致之传。则经文第一大文第四大文之间。了无关锁上下从容不迫之意味。如人之斲落两齿者。顿觉虚疏。当以知止而后有定一节。为三纲领之结语。物有本末一节。置之于国治而天下平之下。为八条目之结语。又以传四章听讼一节。置之于物有本末之下。以为三纲领八条目之总结。然后次第条理。似为明白矣。晦斋尝以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略与愚见相同。而但既以知止而后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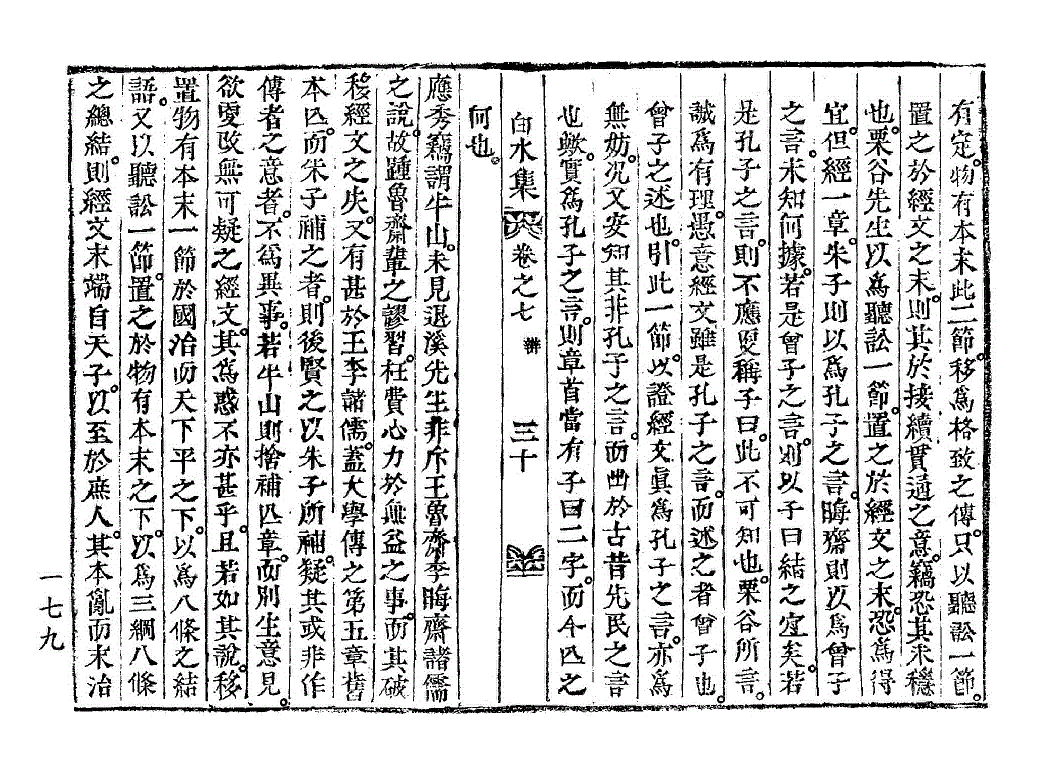 有定。物有本末此二节。移为格致之传。只以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则其于接续贯通之意。窃恐其未稳也。栗谷先生以为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恐为得宜。但经一章。朱子则以为孔子之言。晦斋则以为曾子之言。未知何据。若是曾子之言。则以子曰结之宜矣。若是孔子之言。则不应更称子曰。此不可知也。栗谷所言。诚为有理。愚意经文虽是孔子之言。而述之者曾子也。曾子之述也。引此一节。以證经文真为孔子之言。亦为无妨。况又安知其非孔子之言。而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欤。实为孔子之言。则章首当有子曰二字。而今亡之何也。
有定。物有本末此二节。移为格致之传。只以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则其于接续贯通之意。窃恐其未稳也。栗谷先生以为听讼一节。置之于经文之末。恐为得宜。但经一章。朱子则以为孔子之言。晦斋则以为曾子之言。未知何据。若是曾子之言。则以子曰结之宜矣。若是孔子之言。则不应更称子曰。此不可知也。栗谷所言。诚为有理。愚意经文虽是孔子之言。而述之者曾子也。曾子之述也。引此一节。以證经文真为孔子之言。亦为无妨。况又安知其非孔子之言。而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欤。实为孔子之言。则章首当有子曰二字。而今亡之何也。应秀窃谓牛山。未见退溪先生非斥王鲁斋,李晦斋诸儒之说。故踵鲁斋辈之谬习。枉费心力于无益之事。而其破移经文之失。又有甚于王李诸儒。盖大学传之第五章旧本亡。而朱子补之者。则后贤之以朱子所补。疑其或非作传者之意者。不为异事。若牛山则舍补亡章。而别生意见。欲更改无可疑之经文。其为惑不亦甚乎。且若如其说。移置物有本末一节于国治而天下平之下。以为八条之结语。又以听讼一节。置之于物有本末之下。以为三纲八条之总结。则经文末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本乱而末治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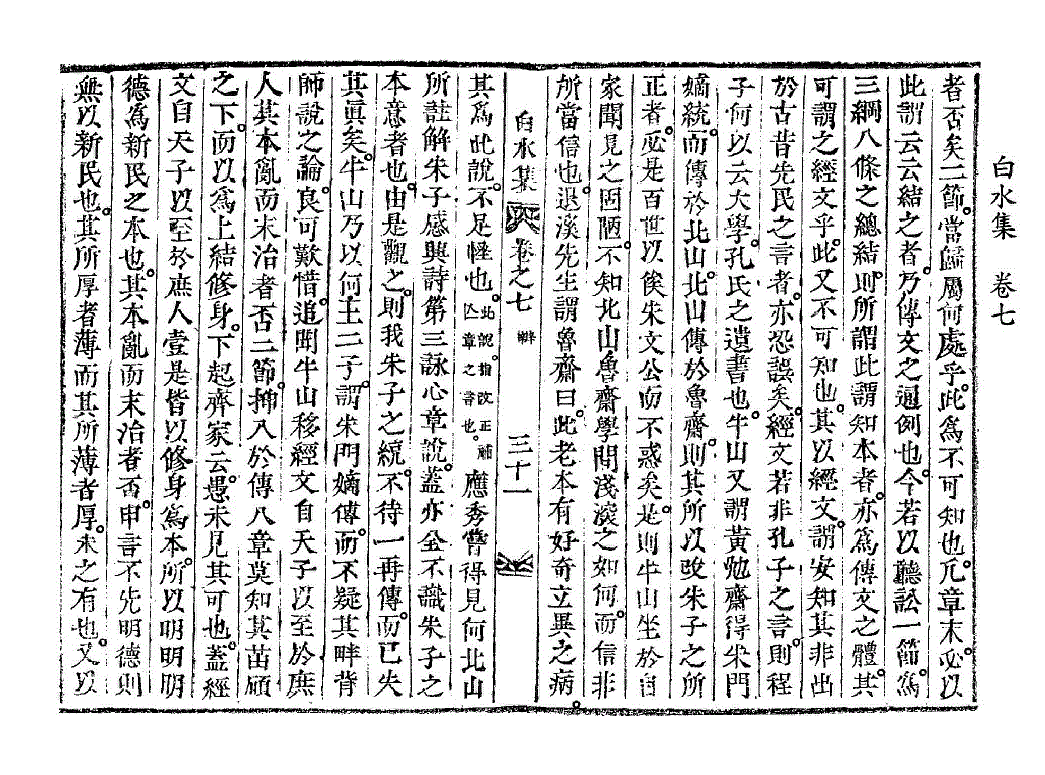 者否矣二节。当归属何处乎。此为不可知也。凡章末。必以此谓云云结之者。乃传文之通例也。今若以听讼一节。为三纲八条之总结。则所谓此谓知本者。亦为传文之体。其可谓之经文乎。此又不可知也。其以经文。谓安知其非出于古昔先民之言者。亦恐误矣。经文若非孔子之言。则程子何以云大学。孔氏之遗书也。牛山又谓黄勉斋得朱门嫡统。而传于北山。北山传于鲁斋。则其所以改朱子之所正者。必是百世以俟朱文公而不惑矣。是则牛山坐于自家闻见之固陋。不知北山,鲁斋学问浅深之如何。而信非所当信也。退溪先生谓鲁斋曰。此老本有好奇立异之病。其为此说。不足怪也。(此说。指改正补亡章之言也。)应秀尝得见何北山所注解朱子感兴诗第三咏心章说。盖亦全不识朱子之本意者也。由是观之。则我朱子之统。不待一再传。而已失其真矣。牛山乃以何,王二子。谓朱门嫡传。而不疑其畔背师说之论。良可叹惜。追闻牛山移经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二节。插入于传八章莫知其苗硕之下。而以为上结修身。下起齐家云。愚未见其可也。盖经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明明明德为新民之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申言不先明德则无以新民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以
者否矣二节。当归属何处乎。此为不可知也。凡章末。必以此谓云云结之者。乃传文之通例也。今若以听讼一节。为三纲八条之总结。则所谓此谓知本者。亦为传文之体。其可谓之经文乎。此又不可知也。其以经文。谓安知其非出于古昔先民之言者。亦恐误矣。经文若非孔子之言。则程子何以云大学。孔氏之遗书也。牛山又谓黄勉斋得朱门嫡统。而传于北山。北山传于鲁斋。则其所以改朱子之所正者。必是百世以俟朱文公而不惑矣。是则牛山坐于自家闻见之固陋。不知北山,鲁斋学问浅深之如何。而信非所当信也。退溪先生谓鲁斋曰。此老本有好奇立异之病。其为此说。不足怪也。(此说。指改正补亡章之言也。)应秀尝得见何北山所注解朱子感兴诗第三咏心章说。盖亦全不识朱子之本意者也。由是观之。则我朱子之统。不待一再传。而已失其真矣。牛山乃以何,王二子。谓朱门嫡传。而不疑其畔背师说之论。良可叹惜。追闻牛山移经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二节。插入于传八章莫知其苗硕之下。而以为上结修身。下起齐家云。愚未见其可也。盖经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明明明德为新民之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申言不先明德则无以新民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以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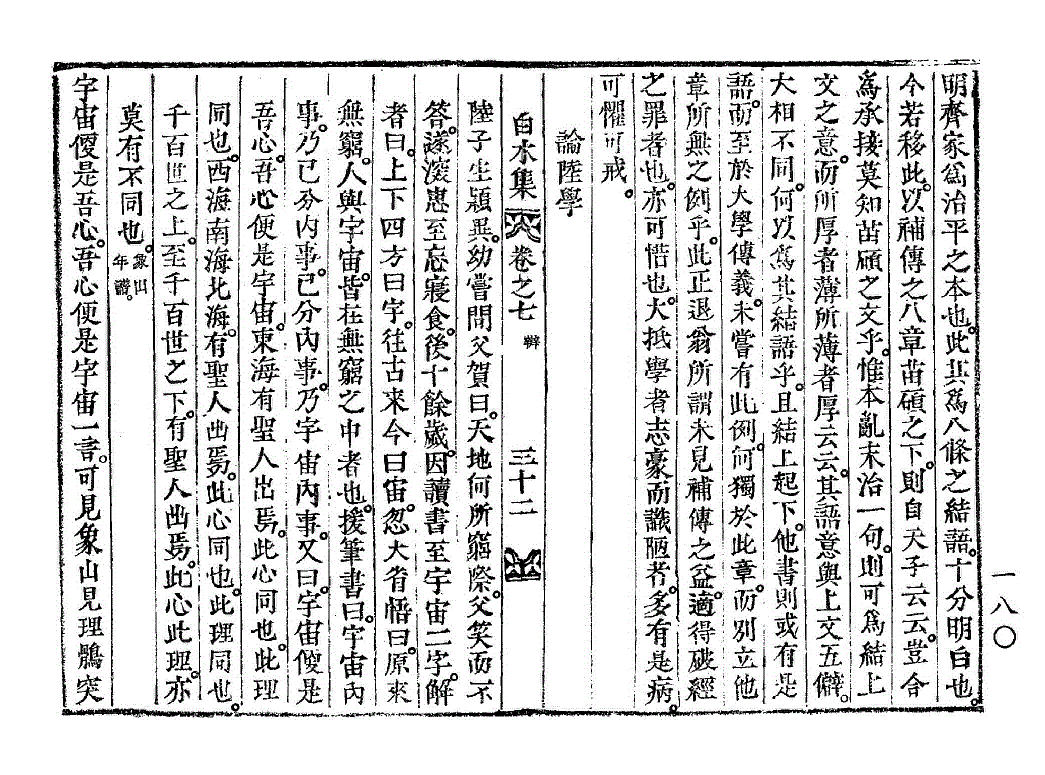 明齐家为治平之本也。此其为八条之结语。十分明白也。今若移此。以补传之八章苗硕之下。则自天子云云。岂合为承接莫知苗硕之文乎。惟本乱末治一句。则可为结上文之意。而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云云。其语意与上文五僻。大相不同。何以为其结语乎。且结上起下。他书则或有是语。而至于大学传义。未尝有此例。何独于此章。而别立他章所无之例乎。此正退翁所谓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者也。亦可惜也。大抵学者志豪而识陋者。多有是病。可惧可戒。
明齐家为治平之本也。此其为八条之结语。十分明白也。今若移此。以补传之八章苗硕之下。则自天子云云。岂合为承接莫知苗硕之文乎。惟本乱末治一句。则可为结上文之意。而所厚者薄所薄者厚云云。其语意与上文五僻。大相不同。何以为其结语乎。且结上起下。他书则或有是语。而至于大学传义。未尝有此例。何独于此章。而别立他章所无之例乎。此正退翁所谓未见补传之益。适得破经之罪者也。亦可惜也。大抵学者志豪而识陋者。多有是病。可惧可戒。论陆学
陆子生颖异。幼尝问父贺曰。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寝食。后十馀岁。因读书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来无穷。人与宇宙。皆在无穷之中者也。援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象山年谱)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一言。可见象山见理鹘突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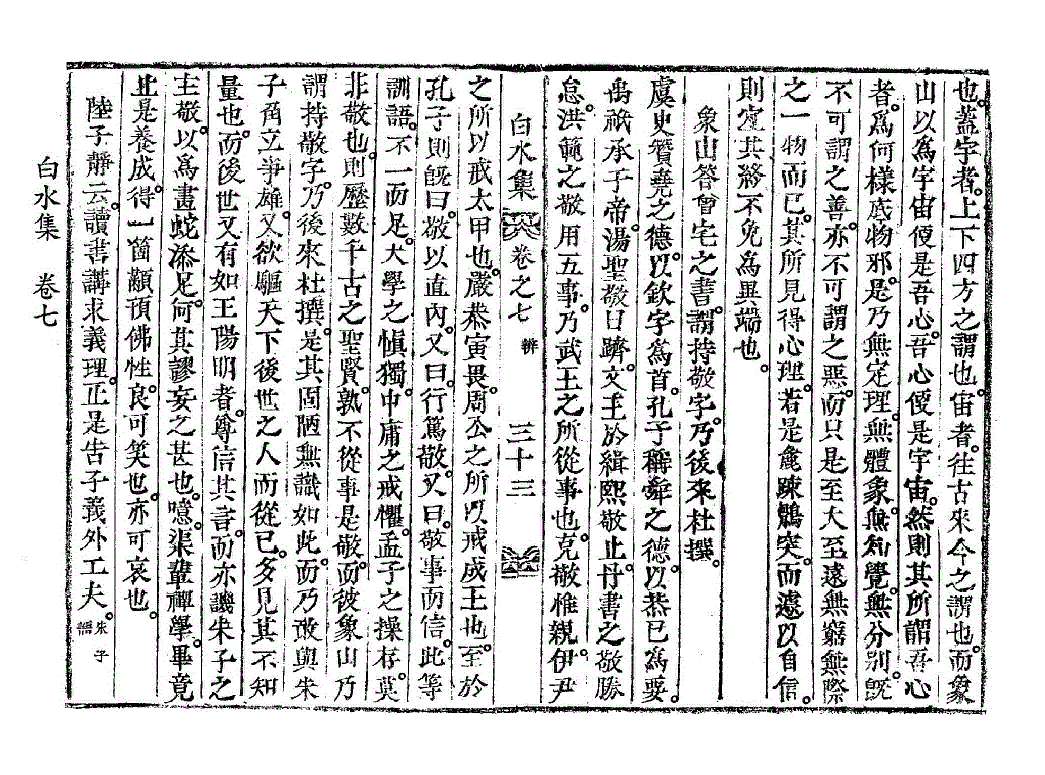 也。盖宇者。上下四方之谓也。宙者。往古来今之谓也。而象山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然则其所谓吾心者。为何样底物邪。是乃无定理。无体象。无知觉。无分别。既不可谓之善。亦不可谓之恶。而只是至大至远无穷无际之一物而已。其所见得心理。若是粗疏鹘突。而遽以自信。则宜其终不免为异端也。
也。盖宇者。上下四方之谓也。宙者。往古来今之谓也。而象山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然则其所谓吾心者。为何样底物邪。是乃无定理。无体象。无知觉。无分别。既不可谓之善。亦不可谓之恶。而只是至大至远无穷无际之一物而已。其所见得心理。若是粗疏鹘突。而遽以自信。则宜其终不免为异端也。象山答曾宅之书。谓持敬字。乃后来杜撰。
虞史赞尧之德。以钦字为首。孔子称舜之德。以恭己为要。禹祇承于帝。汤圣敬日跻。文王于缉熙敬止。丹书之敬胜怠。洪范之敬用五事。乃武王之所从事也。克敬惟亲。伊尹之所以戒太甲也。严恭寅畏。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至于孔子则既曰。敬以直内。又曰。行笃敬。又曰。敬事而信。此等训语。不一而足。大学之慎独。中庸之戒惧。孟子之操存。莫非敬也。则历数千古之圣贤。孰不从事是敬。而彼象山乃谓持敬字。乃后来杜撰。是其固陋无识如此。而乃敢与朱子角立争雄。又欲驱天下后世之人而从己。多见其不知量也。而后世又有如王阳明者。尊信其言。而亦讥朱子之主敬。以为画蛇添足。何其谬妄之甚也。噫。渠辈禅学。毕竟止是养成。得一个颟顸佛性。良可笑也。亦可哀也。
陆子静云。读书讲求义理。正是告子义外工夫。(朱子语)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1L 页
 于此一言。尤可见陆学之为异端也。孔子尝读易。韦编三绝。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非圣人读书求义理之事乎。其教颜子。则先博之以文。后约之以礼。其教伯鱼。则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学礼。无以立。其于大畜象辞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于兑卦象辞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此亦莫非教人读书讲求义理也。彼陆氏则乃以读书讲求义理。谓之告子义外工夫。此非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道者乎。
于此一言。尤可见陆学之为异端也。孔子尝读易。韦编三绝。又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非圣人读书求义理之事乎。其教颜子。则先博之以文。后约之以礼。其教伯鱼。则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学礼。无以立。其于大畜象辞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于兑卦象辞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此亦莫非教人读书讲求义理也。彼陆氏则乃以读书讲求义理。谓之告子义外工夫。此非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道者乎。陆子曰。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象山语录)
愚谓无事时。当完养精神。有事时。当著精神于事。以执厥中。若屏绝事为而专务完养精神。则是一生无是处也。如使陆子。当大禹治水之事。则能不如禹之劳身焦思。而全要精神在内乎。异端所见之偏。每每如是。而不自觉其为非以误其一生。其可哀哉。
杨慈湖(名简。字敬仲。象山门人。)行状云。慈湖初在大学循理斋。尝入夜忆先训。默自反己。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非吾心外事。至陆先生新第。归来富阳。慈湖留之。夜集双明阁上。数提本心二字。因从容问曰。何为本心。适平朝。尝听扇讼。陆先生即扬声答曰。适断扇讼。见得孰是孰非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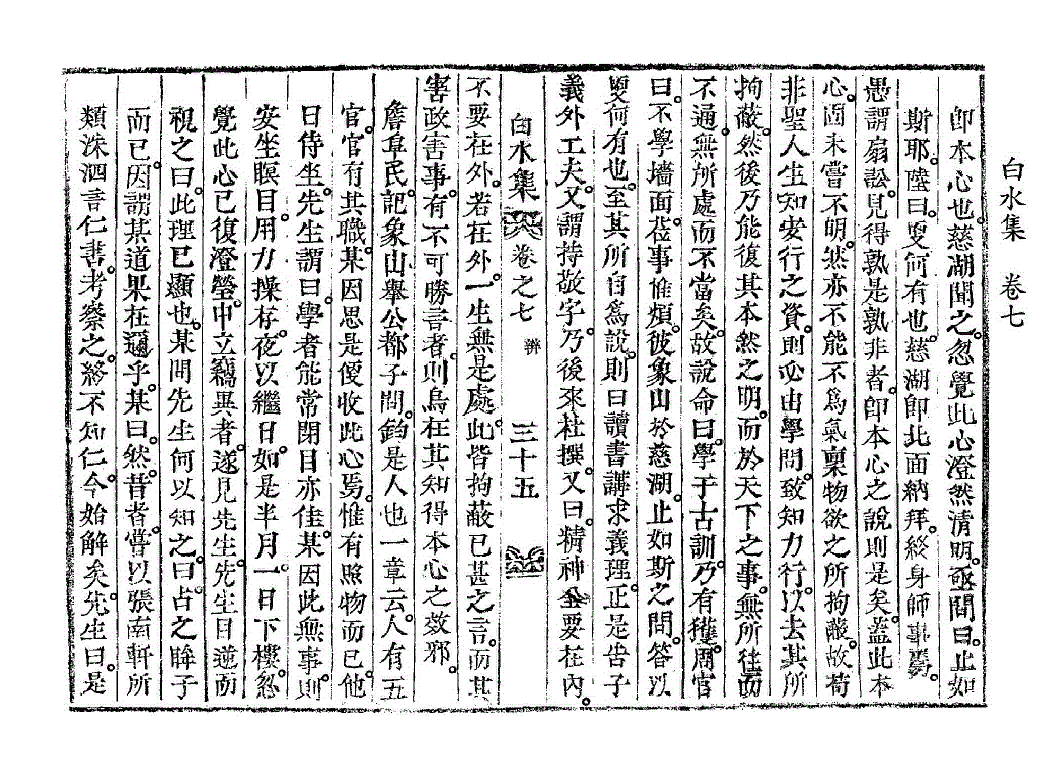 即本心也。慈湖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耶。陆曰。更何有也。慈湖即北面纳拜。终身师事焉。
即本心也。慈湖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耶。陆曰。更何有也。慈湖即北面纳拜。终身师事焉。愚谓扇讼。见得孰是孰非者。即本心之说则是矣。盖此本心。固未尝不明。然亦不能不为气禀物欲之所拘蔽。故苟非圣人生知安行之资。则必由学问。致知力行。以去其所拘蔽。然后乃能复其本然之明。而于天下之事。无所往而不通。无所处而不当矣。故说命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周官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彼象山于慈湖。止如斯之问。答以更何有也。至其所自为说。则曰读书讲求义理。正是告子义外工夫。又谓持敬字。乃后来杜撰。又曰。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此皆拘蔽已甚之言。而其害政害事。有不可胜言者。则乌在其知得本心之效邪。
詹阜民。记象山举公都子问。钧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职。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焉。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谓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则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继日。如是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窃异者。遂见先生。先生目逆而视之曰。此理已显也。某问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谓某道果在迩乎。某曰。然。昔者。尝以张南轩所类洙泗言仁书。考察之。终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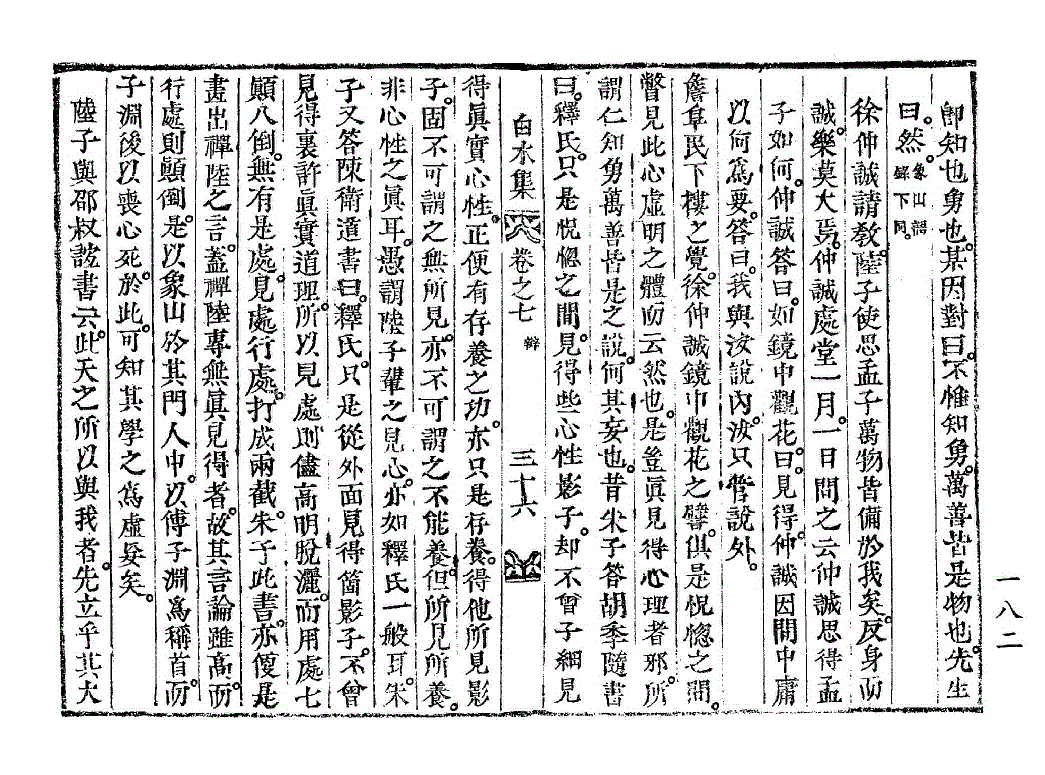 即知也勇也。某因对曰。不惟知勇。万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语录下同)
即知也勇也。某因对曰。不惟知勇。万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象山语录下同)徐仲诚请教。陆子使思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仲诚处堂一月。一日问之云仲诚思得孟子如何。仲诚答曰。如镜中观花。曰。见得。仲诚因问中庸以何为要。答曰。我与汝说内。汝只管说外。
詹阜民下楼之觉。徐仲诚镜中观花之譬。俱是恍惚之间。瞥见此心虚明之体而云然也。是岂真见得心理者邪。所谓仁知勇万善皆是之说。何其妄也。昔朱子答胡季随书曰。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正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愚谓陆子辈之见心。亦如释氏一般耳。朱子又答陈卫道书曰。释氏。只是从外面见得个影子。不曾见得里许真实道理。所以见处。则尽高明脱洒。而用处七颠八倒。无有是处。见处行处。打成两截。朱子此书。亦便是画出禅陆之言。盖禅陆专无真见得者。故其言论虽高。而行处则颠倒。是以象山于其门人中。以傅子渊为称首。而子渊后以丧心死。于此。可知其学之为虚妄矣。
陆子与邵叔谊书云。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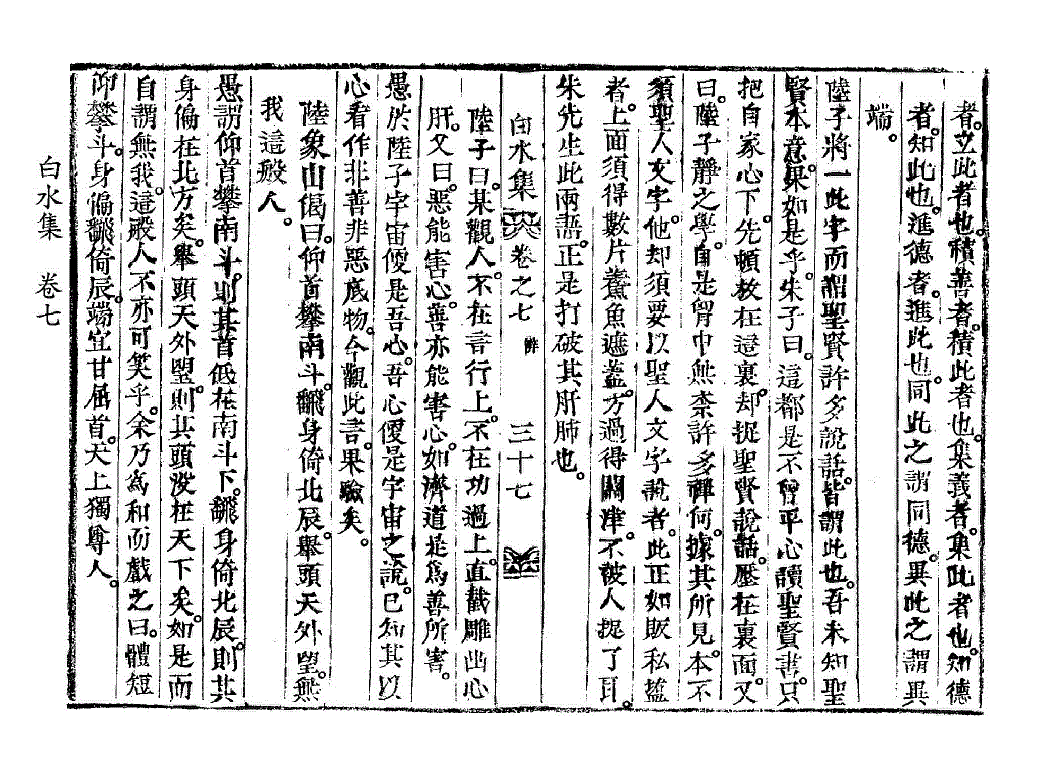 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也。进德者。进此也。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
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也。进德者。进此也。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陆子将一此字而谓圣贤许多说话。皆谓此也。吾未知圣贤本意。果如是乎。朱子曰。这都是不曾平心读圣贤书。只把自家心下。先顿放在这里。却捉圣贤说话。压在里面。又曰。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柰许多禅何。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私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朱先生此两语。正是打破其肝肺也。
陆子曰。某观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过上。直截雕出心肝。又曰。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济道是为善所害。
愚于陆子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说。已知其以心看作非善非恶底物。今观此言。果验矣。
陆象山偈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愚谓仰首攀南斗。则其首低在南斗下。翻身倚北辰。则其身偏在北方矣。举头天外望。则其头没在天下矣。如是而自谓无我。这般人不亦可笑乎。余乃为和而戏之曰。体短仰攀斗。身偏翻倚辰。端宜甘屈首。天上独尊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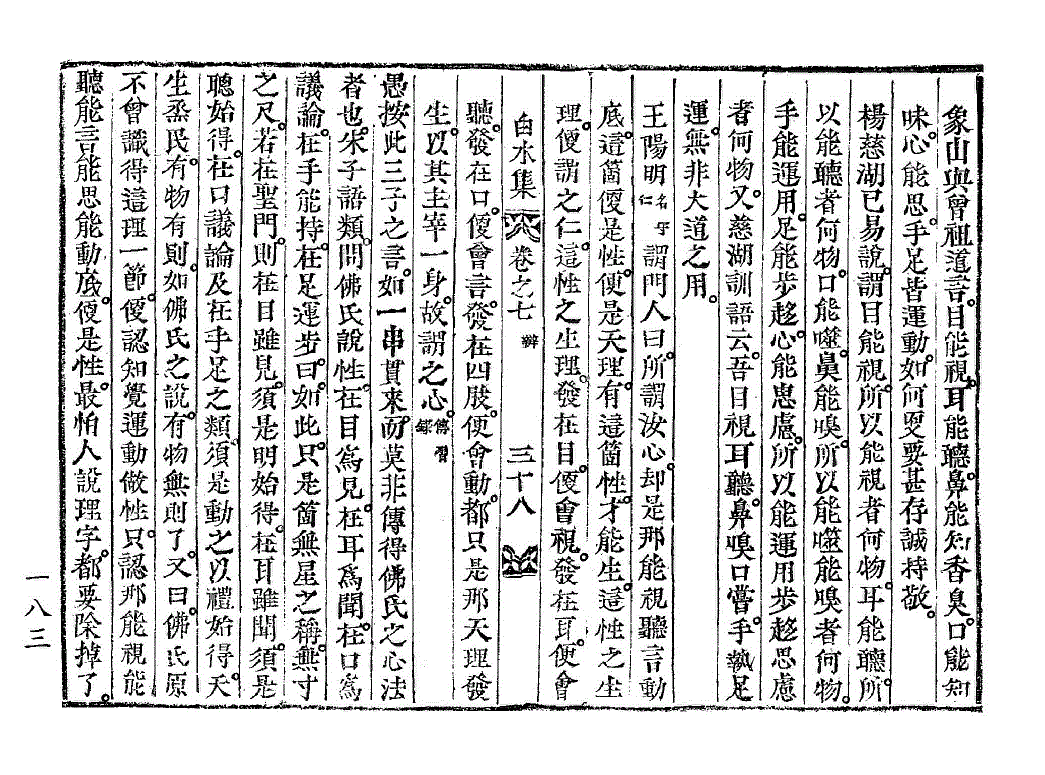 象山与曾祖道言。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皆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
象山与曾祖道言。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皆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杨慈湖已易说。谓目能视。所以能视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鼻能嗅。所以能噬能嗅者何物。手能运用。足能步趍。心能思虑。所以能运用步趍思虑者何物。又慈湖训语云。吾目视耳听。鼻嗅口尝。手执足运。无非大道之用。
王阳明(名守仁)谓门人曰。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底。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传习录)
愚按此三子之言。如一串贯来。而莫非传得佛氏之心法者也。朱子语类。问佛氏说性。在目为见。在耳为闻。在口为议论。在手能持。在足运步。曰。如此。只是个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若在圣门。则在目虽见。须是明始得。在耳虽闻。须是聪始得。在口议论及在手足之类。须是动之以礼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佛氏之说。有物无则了。又曰。佛氏原不曾识得这理一节。便认知觉运动做性。只认那能视能听能言能思能动底。便是性。最怕人说理字。都要除掉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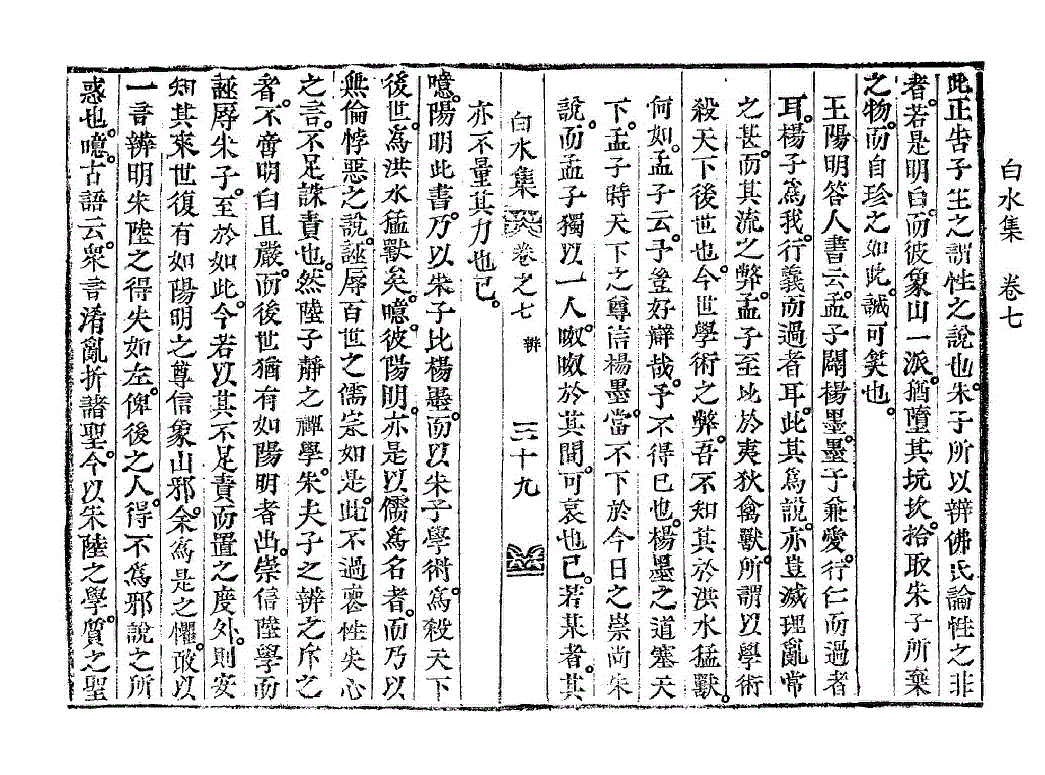 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朱子所以辨佛氏论性之非者。若是明白。而彼象山一派。犹堕其坑坎。拾取朱子所弃之物。而自珍之如此。诚可笑也。
此正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朱子所以辨佛氏论性之非者。若是明白。而彼象山一派。犹堕其坑坎。拾取朱子所弃之物。而自珍之如此。诚可笑也。王阳明答人书云。孟子辟杨墨。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者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者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夷狄禽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可哀也已。若某者。其亦不量其力也已。
噫。阳明此书。乃以朱子比杨墨。而以朱子学术。为杀天下后世。为洪水猛兽矣。噫。彼阳明。亦是以儒为名者。而乃以无伦悖恶之说。诬辱百世之儒宗如是。此不过丧性失心之言。不足诛责也。然陆子静之禅学。朱夫子之辨之斥之者。不啻明白且严。而后世犹有如阳明者出。崇信陆学而诬辱朱子。至于如此。今若以其不足责而置之度外。则安知其来世复有如阳明之尊信象山邪。余为是之惧。敢以一言辨明朱陆之得失如左。俾后之人。得不为邪说之所惑也。噫。古语云。众言淆乱折诸圣。今以朱陆之学。质之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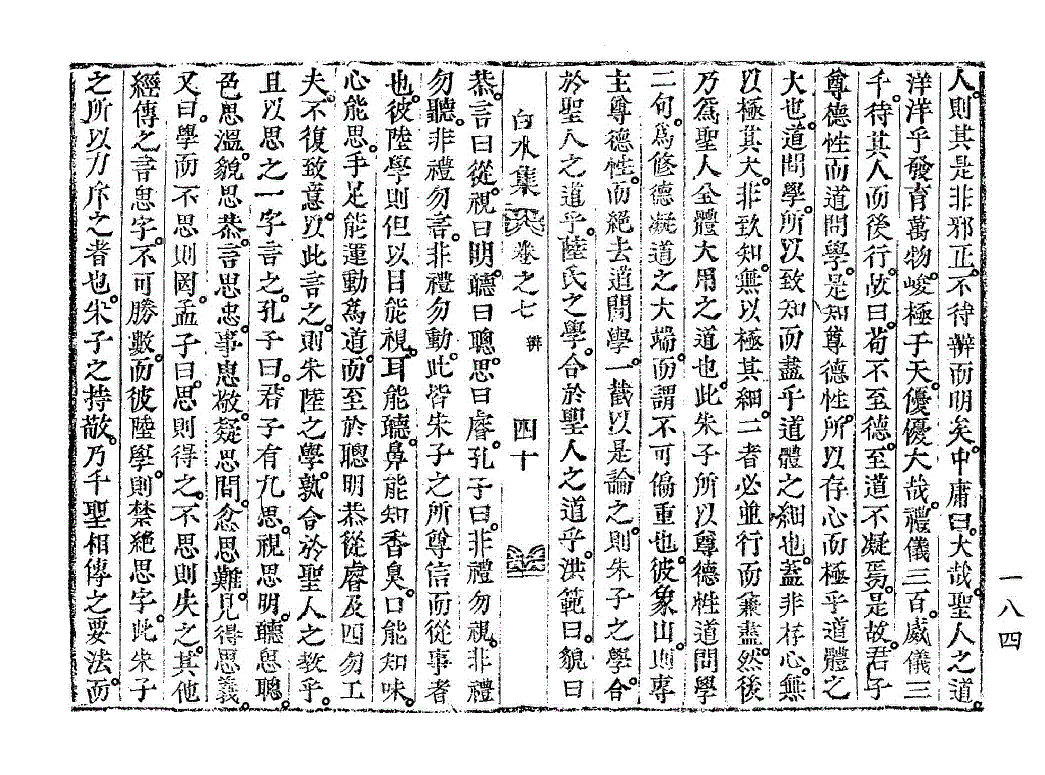 人。则其是非邪正。不待辨而明矣。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盖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非致知。无以极其细。二者必并行而兼尽。然后乃为圣人全体大用之道也。此朱子所以尊德性道问学二句。为修德凝道之大端。而谓不可偏重也。彼象山。则专主尊德性。而绝去道问学。一截以是论之。则朱子之学。合于圣人之道乎。陆氏之学。合于圣人之道乎。洪范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皆朱子之所尊信而从事者也。彼陆学则但以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为道。而至于聪明恭从睿及四勿工夫。不复致意。以此言之。则朱陆之学。孰合于圣人之教乎。且以思之一字言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又曰。学而不思则罔。孟子曰。思则得之。不思则失之。其他经传之言思字。不可胜数。而彼陆学。则禁绝思字。此朱子之所以力斥之者也。朱子之持敬。乃千圣相传之要法。而
人。则其是非邪正。不待辨而明矣。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是知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盖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非致知。无以极其细。二者必并行而兼尽。然后乃为圣人全体大用之道也。此朱子所以尊德性道问学二句。为修德凝道之大端。而谓不可偏重也。彼象山。则专主尊德性。而绝去道问学。一截以是论之。则朱子之学。合于圣人之道乎。陆氏之学。合于圣人之道乎。洪范曰。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皆朱子之所尊信而从事者也。彼陆学则但以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为道。而至于聪明恭从睿及四勿工夫。不复致意。以此言之。则朱陆之学。孰合于圣人之教乎。且以思之一字言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又曰。学而不思则罔。孟子曰。思则得之。不思则失之。其他经传之言思字。不可胜数。而彼陆学。则禁绝思字。此朱子之所以力斥之者也。朱子之持敬。乃千圣相传之要法。而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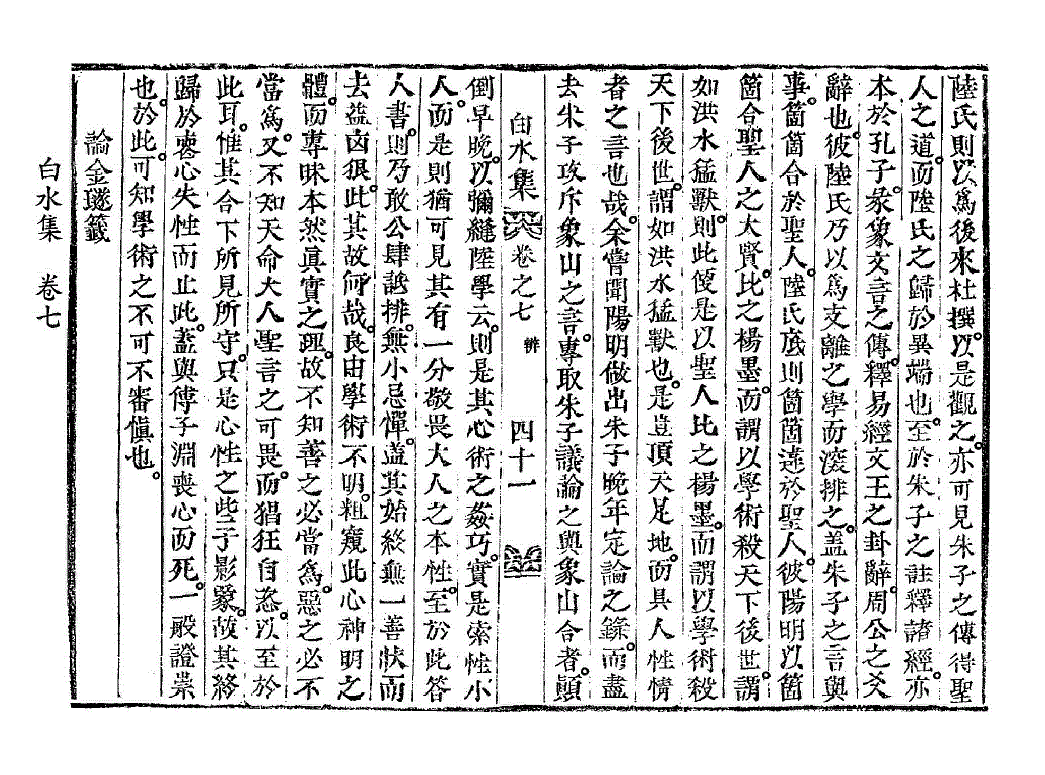 陆氏则以为后来杜撰。以是观之。亦可见朱子之传得圣人之道。而陆氏之归于异端也。至于朱子之注释诸经。亦本于孔子。彖象文言之传。释易经文王之卦辞。周公之爻辞也。彼陆氏乃以为支离之学而深排之。盖朱子之言与事。个个合于圣人。陆氏底则个个违于圣人。彼阳明以个个合圣人之大贤。比之杨墨。而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谓如洪水猛兽。则此便是以圣人比之杨墨。而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谓如洪水猛兽也。是岂顶天足地。而具人性情者之言也哉。余尝闻阳明做出朱子晚年定论之录。而尽去朱子攻斥象山之言。专取朱子议论之与象山合者。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云。则是其心术之奸巧。实是索性小人。而是则犹可见其有一分敬畏大人之本性。至于此答人书。则乃敢公肆诋排。无小忌惮。盖其始终无一善状而去益凶狠。此其故何哉。良由学术不明。粗窥此心神明之体。而专昧本然真实之理。故不知善之必当为。恶之必不当为。又不知天命大人圣言之可畏。而猖狂自恣。以至于此耳。惟其合下所见所守。只是心性之些子影象。故其终归于丧心失性而止此。盖与傅子渊丧心而死。一般證祟也。于此。可知学术之不可不审慎也。
陆氏则以为后来杜撰。以是观之。亦可见朱子之传得圣人之道。而陆氏之归于异端也。至于朱子之注释诸经。亦本于孔子。彖象文言之传。释易经文王之卦辞。周公之爻辞也。彼陆氏乃以为支离之学而深排之。盖朱子之言与事。个个合于圣人。陆氏底则个个违于圣人。彼阳明以个个合圣人之大贤。比之杨墨。而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谓如洪水猛兽。则此便是以圣人比之杨墨。而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谓如洪水猛兽也。是岂顶天足地。而具人性情者之言也哉。余尝闻阳明做出朱子晚年定论之录。而尽去朱子攻斥象山之言。专取朱子议论之与象山合者。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云。则是其心术之奸巧。实是索性小人。而是则犹可见其有一分敬畏大人之本性。至于此答人书。则乃敢公肆诋排。无小忌惮。盖其始终无一善状而去益凶狠。此其故何哉。良由学术不明。粗窥此心神明之体。而专昧本然真实之理。故不知善之必当为。恶之必不当为。又不知天命大人圣言之可畏。而猖狂自恣。以至于此耳。惟其合下所见所守。只是心性之些子影象。故其终归于丧心失性而止此。盖与傅子渊丧心而死。一般證祟也。于此。可知学术之不可不审慎也。论金璲签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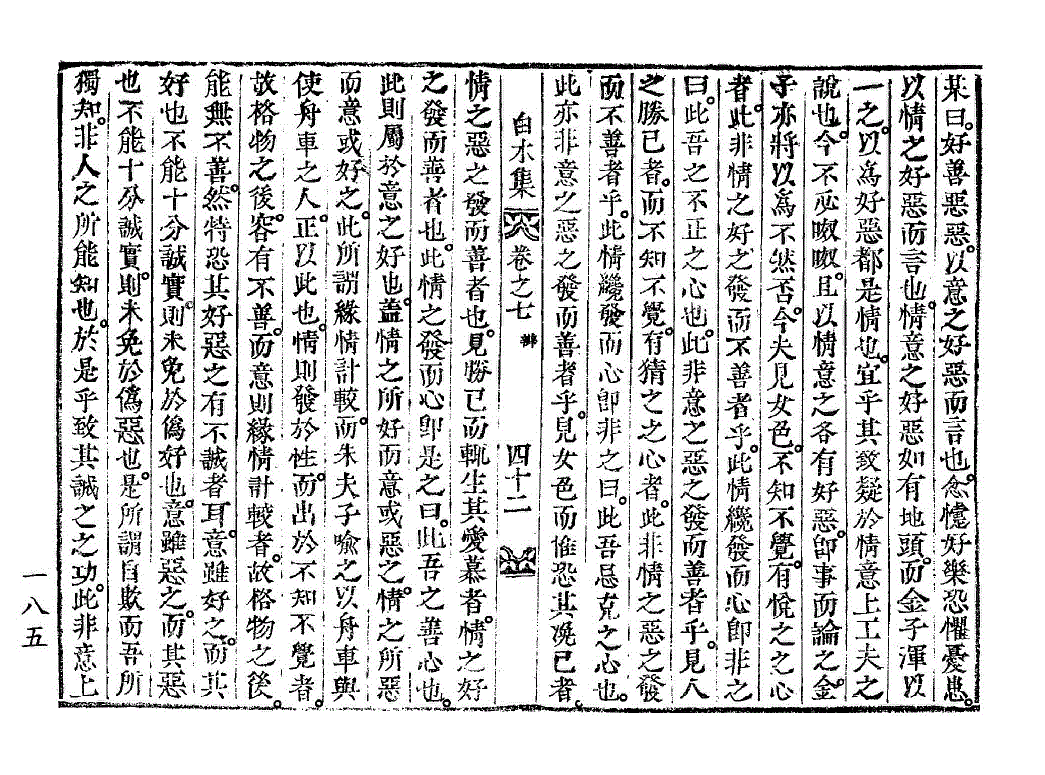 某曰。好善恶恶。以意之好恶而言也。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以情之好恶而言也。情意之好恶如有地头。而金子浑以一之。以为好恶都是情也。宜乎其致疑于情意上工夫之说也。今不必呶呶。且以情意之各有好恶。即事而论之。金子亦将以为不然否。今夫见女色。不知不觉。有悦之之心者。此非情之好之发而不善者乎。此情才发而心即非之曰。此吾之不正之心也。此非意之恶之发而善者乎。见人之胜己者。而不知不觉。有猜之之心者。此非情之恶之发而不善者乎。此情才发而心即非之曰。此吾忌克之心也。此亦非意之恶之发而善者乎。见女色而惟恐其浼己者。情之恶之发而善者也。见胜己而辄生其爱慕者。情之好之发而善者也。此情之发而心即是之曰。此吾之善心也。此则属于意之好也。盖情之所好而意或恶之。情之所恶而意或好之。此所谓缘情计较。而朱夫子喻之以舟车与使舟车之人。正以此也。情则发于性。而出于不知不觉者。故格物之后。容有不善。而意则缘情计较者。故格物之后。能无不善。然特恐其好恶之有不诚者耳。意虽好之。而其好也不能十分诚实。则未免于伪好也。意虽恶之。而其恶也不能十分诚实。则未免于伪恶也。是所谓自欺而吾所独知。非人之所能知也。于是乎致其诚之之功。此非意上
某曰。好善恶恶。以意之好恶而言也。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以情之好恶而言也。情意之好恶如有地头。而金子浑以一之。以为好恶都是情也。宜乎其致疑于情意上工夫之说也。今不必呶呶。且以情意之各有好恶。即事而论之。金子亦将以为不然否。今夫见女色。不知不觉。有悦之之心者。此非情之好之发而不善者乎。此情才发而心即非之曰。此吾之不正之心也。此非意之恶之发而善者乎。见人之胜己者。而不知不觉。有猜之之心者。此非情之恶之发而不善者乎。此情才发而心即非之曰。此吾忌克之心也。此亦非意之恶之发而善者乎。见女色而惟恐其浼己者。情之恶之发而善者也。见胜己而辄生其爱慕者。情之好之发而善者也。此情之发而心即是之曰。此吾之善心也。此则属于意之好也。盖情之所好而意或恶之。情之所恶而意或好之。此所谓缘情计较。而朱夫子喻之以舟车与使舟车之人。正以此也。情则发于性。而出于不知不觉者。故格物之后。容有不善。而意则缘情计较者。故格物之后。能无不善。然特恐其好恶之有不诚者耳。意虽好之。而其好也不能十分诚实。则未免于伪好也。意虽恶之。而其恶也不能十分诚实。则未免于伪恶也。是所谓自欺而吾所独知。非人之所能知也。于是乎致其诚之之功。此非意上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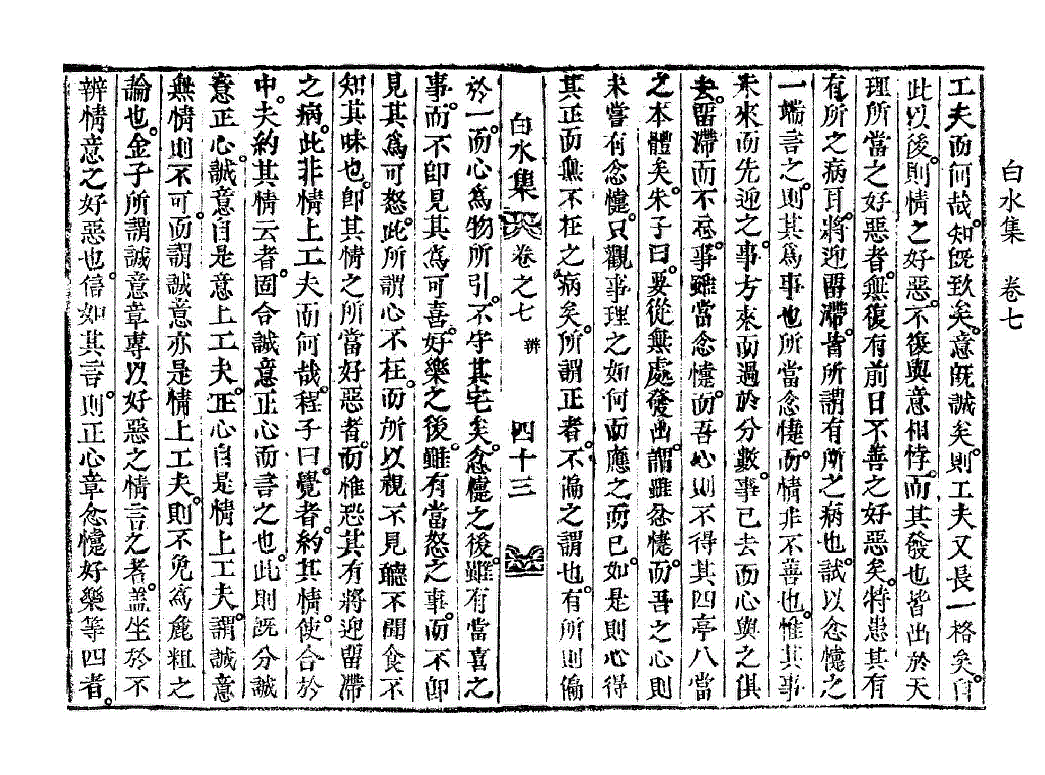 工夫而何哉。知既致矣。意既诚矣。则工夫又长一格矣。自此以后。则情之好恶。不复与意相悖。而其发也皆出于天理所当之好恶者。无复有前日不善之好恶矣。特患其有有所之病耳。将迎留滞。皆所谓有所之病也。试以忿懥之一端言之。则其为事也所当忿𢜀。而情非不善也。惟其事未来而先迎之。事方来而过于分数。事已去而心与之俱去。留滞而不忘。事虽当忿懥。而吾心则不得其四亭八当之本体矣。朱子曰。要从无处发出。谓虽忿𢜀。而吾之心则未尝有忿懥。只观事理之如何而应之而已。如是则心得其正而无不在之病矣。所谓正者。不偏之谓也。有所则偏于一。而心为物所引。不守其宅矣。忿懥之后。虽有当喜之事。而不即见其为可喜。好乐之后。虽有当怒之事。而不即见其为可怒。此所谓心不在。而所以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其味也。即其情之所当好恶者。而惟恐其有将迎留滞之病。此非情上工夫而何哉。程子曰。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夫约其情云者。固合诚意正心而言之也。此则既分诚意正心。诚意自是意上工夫。正心自是情上工夫。谓诚意无情则不可。而谓诚意亦是情上工夫。则不免为粗粗之论也。金子所谓诚意章专以好恶之情言之者。盖坐于不辨情意之好恶也。信如其言。则正心章忿懥好乐等四者。
工夫而何哉。知既致矣。意既诚矣。则工夫又长一格矣。自此以后。则情之好恶。不复与意相悖。而其发也皆出于天理所当之好恶者。无复有前日不善之好恶矣。特患其有有所之病耳。将迎留滞。皆所谓有所之病也。试以忿懥之一端言之。则其为事也所当忿𢜀。而情非不善也。惟其事未来而先迎之。事方来而过于分数。事已去而心与之俱去。留滞而不忘。事虽当忿懥。而吾心则不得其四亭八当之本体矣。朱子曰。要从无处发出。谓虽忿𢜀。而吾之心则未尝有忿懥。只观事理之如何而应之而已。如是则心得其正而无不在之病矣。所谓正者。不偏之谓也。有所则偏于一。而心为物所引。不守其宅矣。忿懥之后。虽有当喜之事。而不即见其为可喜。好乐之后。虽有当怒之事。而不即见其为可怒。此所谓心不在。而所以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其味也。即其情之所当好恶者。而惟恐其有将迎留滞之病。此非情上工夫而何哉。程子曰。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夫约其情云者。固合诚意正心而言之也。此则既分诚意正心。诚意自是意上工夫。正心自是情上工夫。谓诚意无情则不可。而谓诚意亦是情上工夫。则不免为粗粗之论也。金子所谓诚意章专以好恶之情言之者。盖坐于不辨情意之好恶也。信如其言。则正心章忿懥好乐等四者。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七 第 1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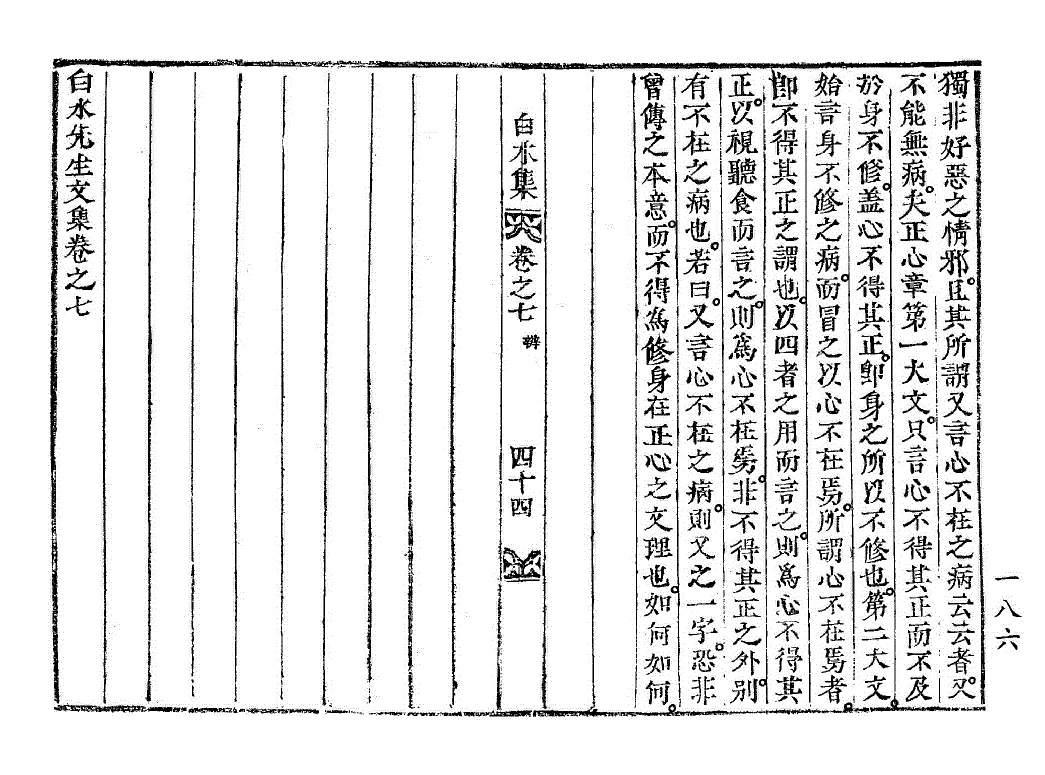 独非好恶之情邪。且其所谓又言心不在之病云云者。又不能无病。夫正心章第一大文。只言心不得其正而不及于身不修。盖心不得其正。即身之所以不修也。第二大文。始言身不修之病。而冒之以心不在焉。所谓心不在焉者。即不得其正之谓也。以四者之用而言之。则为心不得其正。以视听食而言之。则为心不在焉。非不得其正之外。别有不在之病也。若曰。又言心不在之病。则又之一字。恐非曾传之本意。而不得为修身在正心之文理也。如何如何。
独非好恶之情邪。且其所谓又言心不在之病云云者。又不能无病。夫正心章第一大文。只言心不得其正而不及于身不修。盖心不得其正。即身之所以不修也。第二大文。始言身不修之病。而冒之以心不在焉。所谓心不在焉者。即不得其正之谓也。以四者之用而言之。则为心不得其正。以视听食而言之。则为心不在焉。非不得其正之外。别有不在之病也。若曰。又言心不在之病。则又之一字。恐非曾传之本意。而不得为修身在正心之文理也。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