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说
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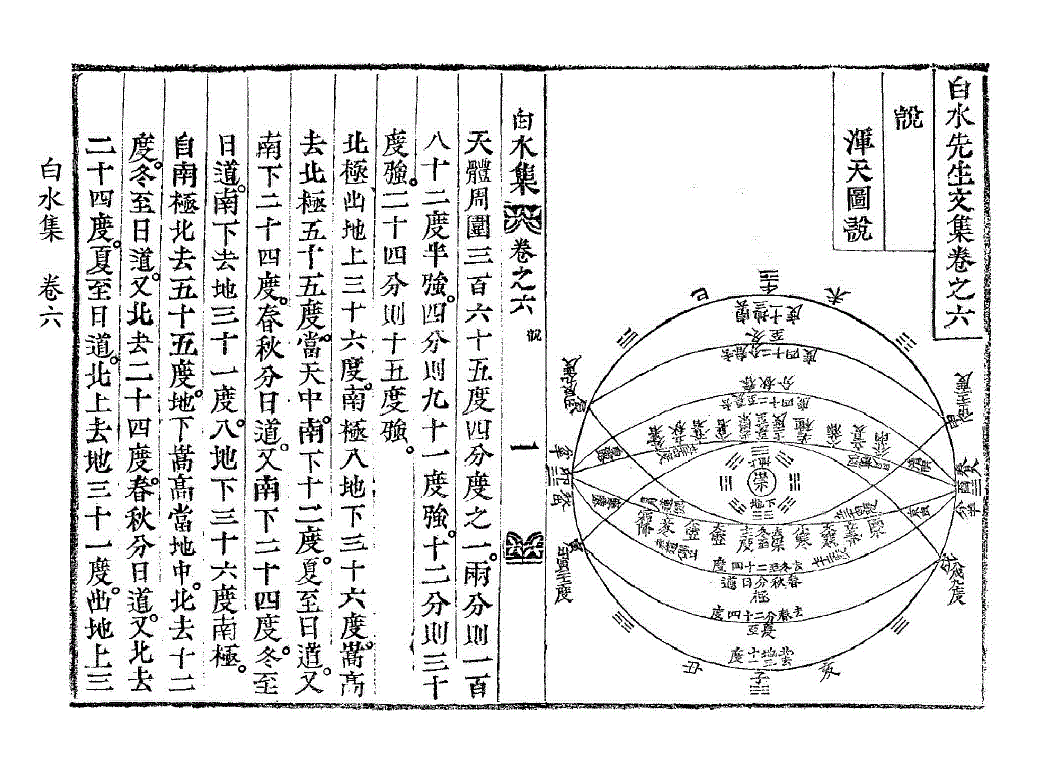 浑天图说
浑天图说삽화 새창열기
天体周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两分则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四分则九十一度强。十二分则三十度强。二十四分则十五度强。
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嵩高去北极五十五度。当天中。南下十二度。夏至日道。又南下二十四度。春秋分日道。又南下二十四度。冬至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极。
自南极北去五十五度。地下嵩高当地中。北去十二度。冬至日道。又北去二十四度。春秋分日道。又北去二十四度。夏至日道。北上去地三十一度。出地上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4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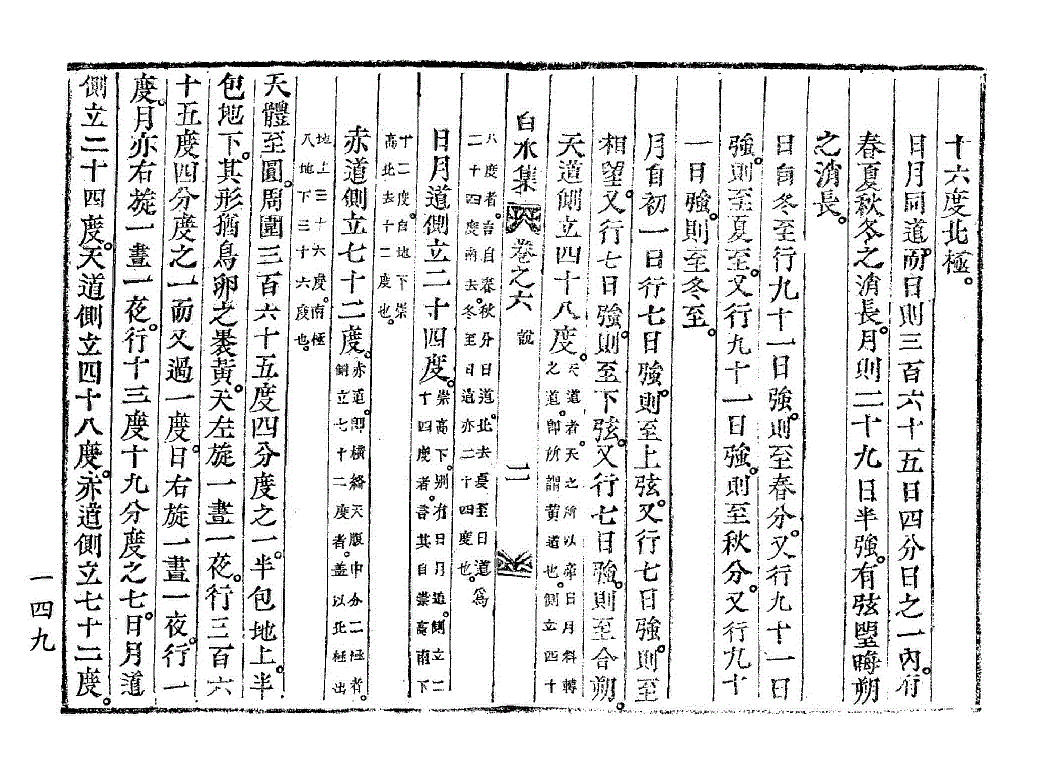 十六度北极。
十六度北极。日月同道。而日则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内。有春夏秋冬之消长。月则二十九日半强。有弦望晦朔之消长。
日自冬至行九十一日强。则至春分。又行九十一日强。则至夏至。又行九十一日强。则至秋分。又行九十一日强。则至冬至。
月自初一日行七日强。则至上弦。又行七日强。则至相望。又行七日强。则至下弦。又行七日强。则至合朔。天道侧立四十八度。(天道者。天之所以牵日月斜转之道。即所谓黄道也。侧立四十八度者。言自春秋分日道。北去夏至日道为二十四度南去。冬至日道亦二十四度也。)
日月道侧立二十四度。(崇高下。别有日月道。侧立二十四度者。言其自崇高南下十二度。自地下崇高北去十二度也。)
赤道侧立七十二度。(赤道。即横络天腹中分二极者。侧立七十二度者。盖以北极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下三十六度也。)
天体至圆。周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包地上。半包地下。其形犹鸟卵之裹黄。天左旋一昼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过一度。日右旋一昼一夜。行一度。月亦右旋一昼一夜。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道侧立二十四度。天道侧立四十八度。赤道侧立七十二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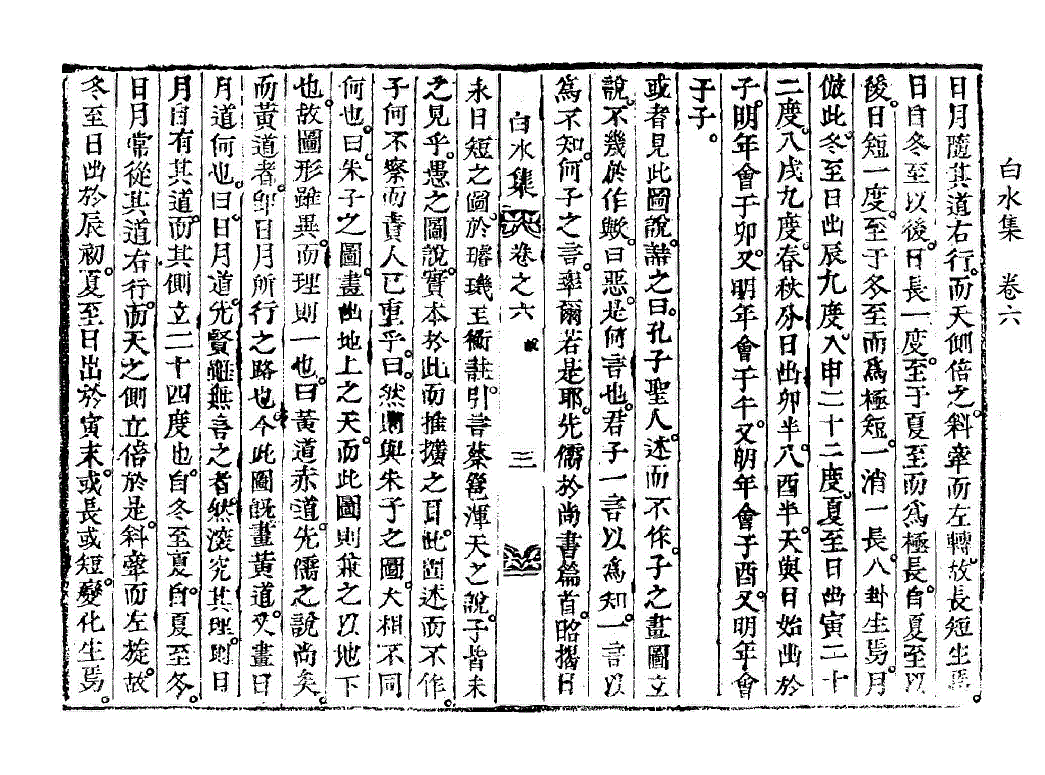 日月随其道右行。而天侧倍之。斜牵而左转。故长短生焉。日自冬至以后。日长一度。至于夏至而为极长。自夏至以后。日短一度。至于冬至而为极短。一消一长。八卦生焉。月仿此。冬至日出辰九度。入申二十二度。夏至日出寅二十二度。入戌九度。春秋分日出卯半。入酉半。天与日始出于子。明年会于卯。又明年会于午。又明年会于酉。又明年会于子。
日月随其道右行。而天侧倍之。斜牵而左转。故长短生焉。日自冬至以后。日长一度。至于夏至而为极长。自夏至以后。日短一度。至于冬至而为极短。一消一长。八卦生焉。月仿此。冬至日出辰九度。入申二十二度。夏至日出寅二十二度。入戌九度。春秋分日出卯半。入酉半。天与日始出于子。明年会于卯。又明年会于午。又明年会于酉。又明年会于子。或者见此图说。诘之曰。孔子圣人。述而不作。子之画图立说。不几于作欤。曰恶。是何言也。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何子之言。率尔若是耶。先儒于尚书篇首。昭揭日永日短之图。于璿玑玉衡注。引言蔡邕浑天之说。子皆未之见乎。愚之图说。实本于此而推扩之耳。此固述而不作。子何不察而责人已重乎。曰。然则与朱子之图。大相不同何也。曰。朱子之图。画出地上之天。而此图则兼之以地下也。故图形虽异。而理则一也。曰黄道赤道。先儒之说尚矣。而黄道者。即日月所行之路也。今此图既画黄道。又画日月道何也。曰。日月道。先贤虽无言之者。然深究其理。则日月自有其道。而其侧立二十四度也。自冬至夏。自夏至冬。日月常从其道右行。而天之侧立倍于是。斜牵而左旋。故冬至日出于辰初。夏至日出于寅末。或长或短。变化生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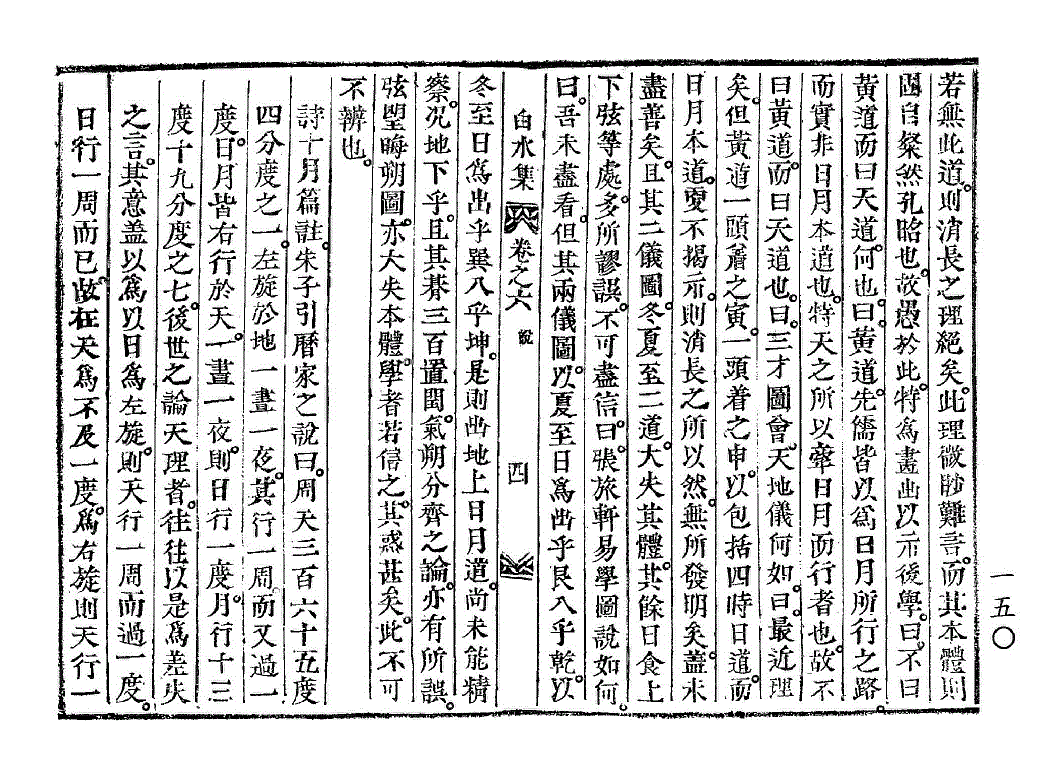 若无此道。则消长之理绝矣。此理微眇难言。而其本体则固自粲然孔昭也。故愚于此。特为画出以示后学。曰。不曰黄道而曰天道。何也。曰。黄道。先儒皆以为日月所行之路。而实非日月本道也。特天之所以牵日月而行者也。故不曰黄道。而曰天道也。曰。三才图会。天地仪何如。曰。最近理矣。但黄道一头着之寅。一头着之申。以包括四时日道。而日月本道。更不揭示。则消长之所以然。无所发明矣。盖未尽善矣。且其二仪图。冬夏至二道。大失其体。其馀日食上下弦等处。多所谬误。不可尽信。曰。张旅轩易学图说如何。曰。吾未尽看。但其两仪图。以夏至日为出乎艮入乎乾。以冬至日为出乎巽入乎坤。是则出地上日月道。尚未能精察。况地下乎。且其期三百置闰。气朔分齐之论。亦有所误。弦望晦朔图。亦大失本体。学者若信之。其惑甚矣。此不可不辨也。
若无此道。则消长之理绝矣。此理微眇难言。而其本体则固自粲然孔昭也。故愚于此。特为画出以示后学。曰。不曰黄道而曰天道。何也。曰。黄道。先儒皆以为日月所行之路。而实非日月本道也。特天之所以牵日月而行者也。故不曰黄道。而曰天道也。曰。三才图会。天地仪何如。曰。最近理矣。但黄道一头着之寅。一头着之申。以包括四时日道。而日月本道。更不揭示。则消长之所以然。无所发明矣。盖未尽善矣。且其二仪图。冬夏至二道。大失其体。其馀日食上下弦等处。多所谬误。不可尽信。曰。张旅轩易学图说如何。曰。吾未尽看。但其两仪图。以夏至日为出乎艮入乎乾。以冬至日为出乎巽入乎坤。是则出地上日月道。尚未能精察。况地下乎。且其期三百置闰。气朔分齐之论。亦有所误。弦望晦朔图。亦大失本体。学者若信之。其惑甚矣。此不可不辨也。诗十月篇注。朱子引历家之说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昼一夜。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一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后世之论天理者。往往以是为差失之言。其意盖以为以日为左旋。则天行一周而过一度。日行一周而已。故在天为不及一度。为右旋则天行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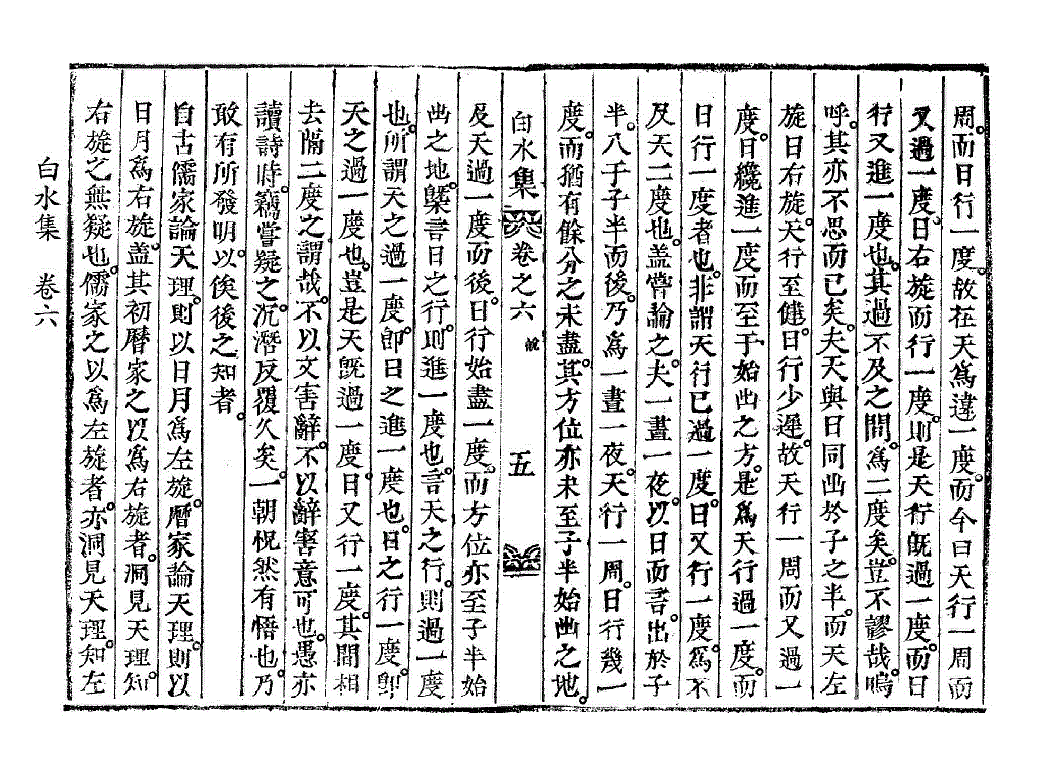 周。而日行一度。故在天为违一度。而今曰天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右旋而行一度。则是天行既过一度。而日行又进一度也。其过不及之间。为二度矣。岂不谬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天与日同出于子之半。而天左旋日右旋。天行至健。日行少迟。故天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才进一度而至于始出之方。是为天行过一度。而日行一度者也。非谓天行已过一度。日又行一度。为不及天二度也。盖尝论之。夫一昼一夜。以日而言。出于子半。入于子半而后。乃为一昼一夜。天行一周。日行几一度。而犹有馀分之未尽。其方位亦未至子半始出之地。及天过一度而后。日行始尽一度。而方位亦至子半始出之地。槩言日之行。则进一度也。言天之行。则过一度也。所谓天之过一度。即日之进一度也。日之行一度。即天之过一度也。岂是天既过一度。日又行一度。其间相去隔二度之谓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可也。愚亦读诗时。窃尝疑之。沉潜反覆久矣。一朝恍然有悟也。乃敢有所发明。以俟后之知者。
周。而日行一度。故在天为违一度。而今曰天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右旋而行一度。则是天行既过一度。而日行又进一度也。其过不及之间。为二度矣。岂不谬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天与日同出于子之半。而天左旋日右旋。天行至健。日行少迟。故天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才进一度而至于始出之方。是为天行过一度。而日行一度者也。非谓天行已过一度。日又行一度。为不及天二度也。盖尝论之。夫一昼一夜。以日而言。出于子半。入于子半而后。乃为一昼一夜。天行一周。日行几一度。而犹有馀分之未尽。其方位亦未至子半始出之地。及天过一度而后。日行始尽一度。而方位亦至子半始出之地。槩言日之行。则进一度也。言天之行。则过一度也。所谓天之过一度。即日之进一度也。日之行一度。即天之过一度也。岂是天既过一度。日又行一度。其间相去隔二度之谓哉。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可也。愚亦读诗时。窃尝疑之。沉潜反覆久矣。一朝恍然有悟也。乃敢有所发明。以俟后之知者。自古儒家论天理。则以日月为左旋。历家论天理。则以日月为右旋。盖其初历家之以为右旋者。洞见天理。知右旋之无疑也。儒家之以为左旋者。亦洞见天理。知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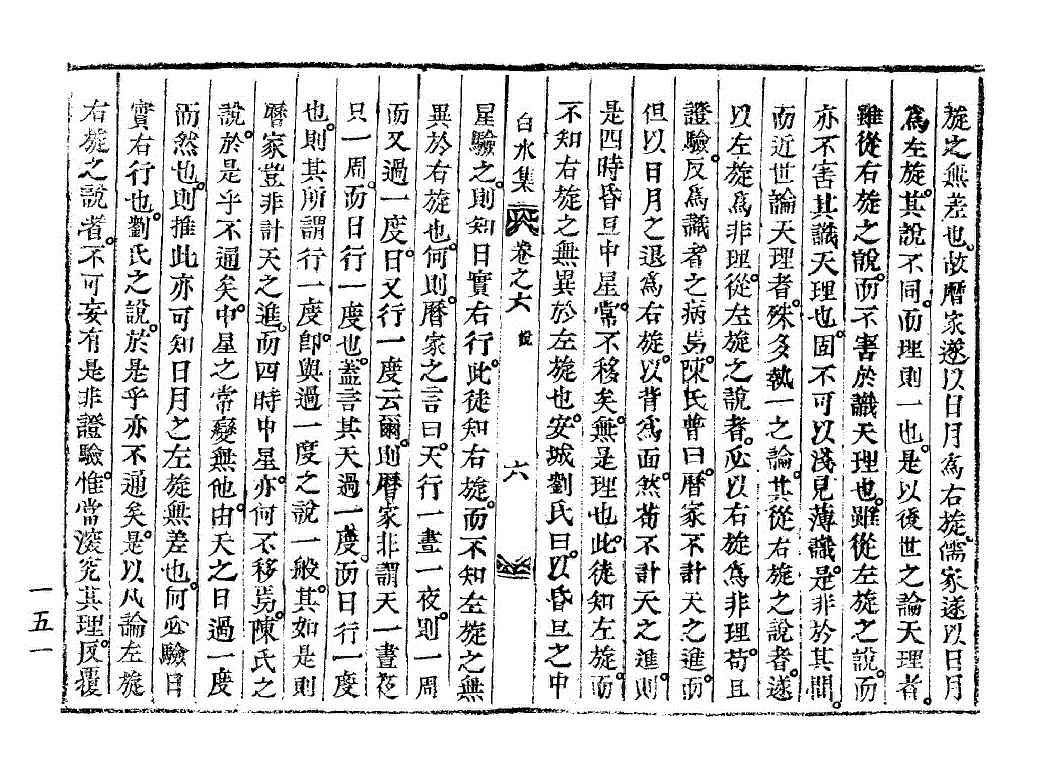 旋之无差也。故历家遂以日月为右旋。儒家遂以日月为左旋。其说不同。而理则一也。是以后世之论天理者。虽从右旋之说。而不害于识天理也。虽从左旋之说。而亦不害其识天理也。固不可以浅见薄识。是非于其间。而近世论天理者。殊多执一之论。其从右旋之说者。遂以左旋为非理。从左旋之说者。必以右旋为非理。苟且證验。反为识者之病焉。陈氏普曰。历家不计天之进。而但以日月之退为右旋。以背为面。然苟不计天之进。则是四时昏旦中星。常不移矣。无是理也。此徒知左旋。而不知右旋之无异于左旋也。安城刘氏曰。以昏旦之中星验之。则知日实右行。此徒知右旋。而不知左旋之无异于右旋也。何则。历家之言曰。天行一昼一夜。则一周而又过一度。日又行一度云尔。则历家非谓天一昼夜只一周。而日行一度也。盖言其天过一度。而日行一度也。则其所谓行一度。即与过一度之说一般。其如是则历家岂非计天之进。而四时中星。亦何不移焉。陈氏之说。于是乎不通矣。中星之常变无他。由天之日过一度而然也。则推此亦可知日月之左旋无差也。何必验日实右行也。刘氏之说。于是乎亦不通矣。是以凡论左旋右旋之说者。不可妄有是非證验。惟当深究其理。反覆
旋之无差也。故历家遂以日月为右旋。儒家遂以日月为左旋。其说不同。而理则一也。是以后世之论天理者。虽从右旋之说。而不害于识天理也。虽从左旋之说。而亦不害其识天理也。固不可以浅见薄识。是非于其间。而近世论天理者。殊多执一之论。其从右旋之说者。遂以左旋为非理。从左旋之说者。必以右旋为非理。苟且證验。反为识者之病焉。陈氏普曰。历家不计天之进。而但以日月之退为右旋。以背为面。然苟不计天之进。则是四时昏旦中星。常不移矣。无是理也。此徒知左旋。而不知右旋之无异于左旋也。安城刘氏曰。以昏旦之中星验之。则知日实右行。此徒知右旋。而不知左旋之无异于右旋也。何则。历家之言曰。天行一昼一夜。则一周而又过一度。日又行一度云尔。则历家非谓天一昼夜只一周。而日行一度也。盖言其天过一度。而日行一度也。则其所谓行一度。即与过一度之说一般。其如是则历家岂非计天之进。而四时中星。亦何不移焉。陈氏之说。于是乎不通矣。中星之常变无他。由天之日过一度而然也。则推此亦可知日月之左旋无差也。何必验日实右行也。刘氏之说。于是乎亦不通矣。是以凡论左旋右旋之说者。不可妄有是非證验。惟当深究其理。反覆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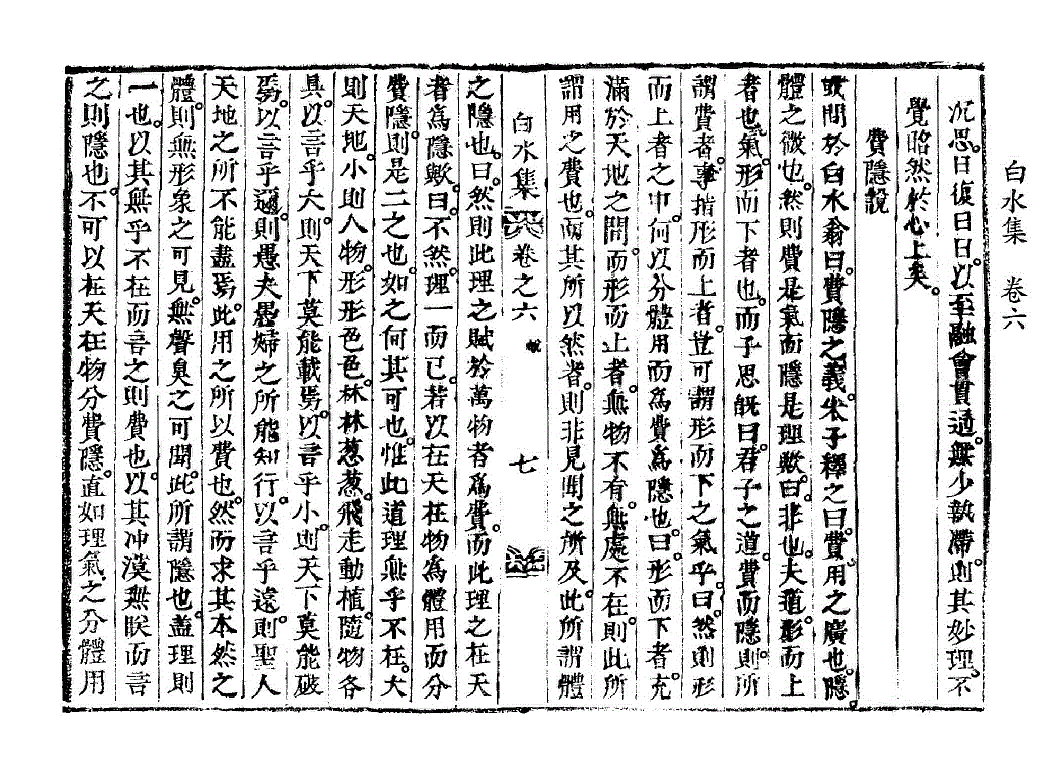 沉思。日复日日。以至融会贯通。无少执滞。则其妙理。不觉昭然于心上矣。
沉思。日复日日。以至融会贯通。无少执滞。则其妙理。不觉昭然于心上矣。费隐说
或问于白水翁曰。费隐之义。朱子释之曰。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然则费是气而隐是理欤。曰。非也。夫道。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而子思既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则所谓费者。专指形而上者。岂可谓形而下之气乎。曰。然则形而上者之中。何以分体用而为费为隐也。曰。形而下者。充满于天地之间。而形而上者。无物不有。无处不在。则此所谓用之费也。而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之所及。此所谓体之隐也。曰。然则此理之赋于万物者为费。而此理之在天者为隐欤。曰。不然。理一而已。若以在天在物为体用而分费隐。则是二之也。如之何其可也。惟此道理无乎不在。大则天地。小则人物。形形色色。林林葱葱。飞走动植。随物各具。以言乎大。则天下莫能载焉。以言乎小。则天下莫能破焉。以言乎迩。则愚夫愚妇之所能知行。以言乎远。则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焉。此用之所以费也。然而求其本然之体。则无形象之可见。无声臭之可闻。此所谓隐也。盖理则一也。以其无乎不在而言之则费也。以其冲漠无眹而言之则隐也。不可以在天在物分费隐。直如理气之分体用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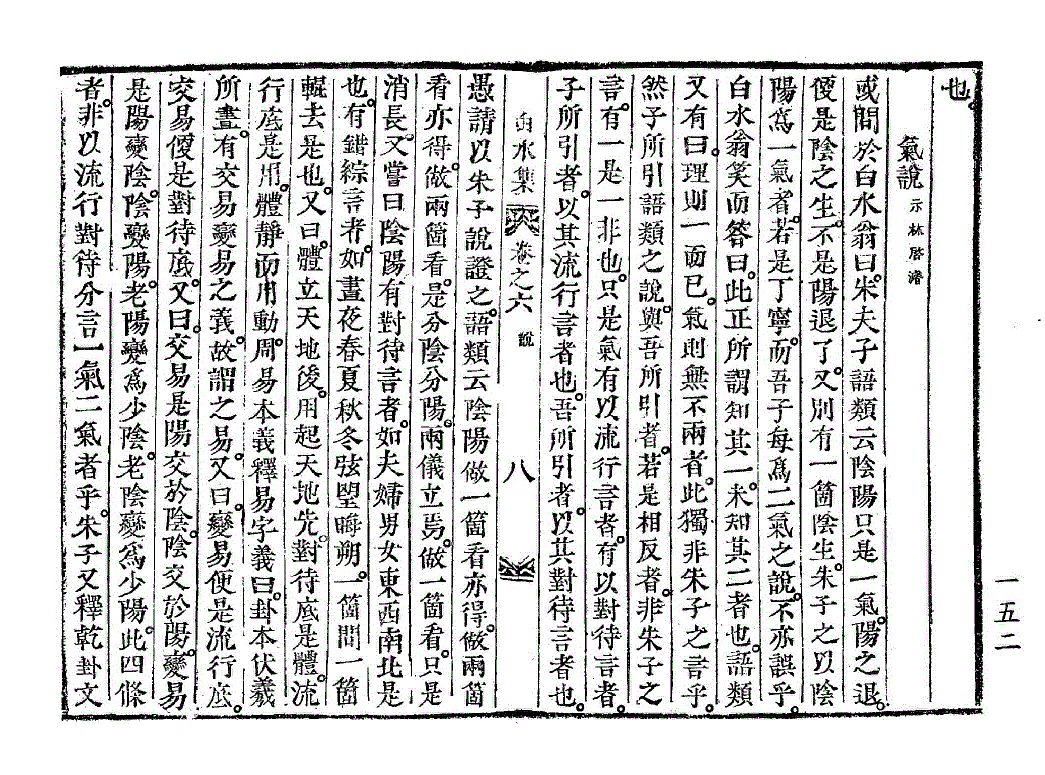 也。
也。气说(示林启浚)
或问于白水翁曰。朱夫子语类云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一个阴生。朱子之以阴阳为一气者。若是丁宁。而吾子每为二气之说。不亦误乎。白水翁笑而答曰。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语类又有曰。理则一而已。气则无不两者。此独非朱子之言乎。然子所引语类之说。与吾所引者。若是相反者。非朱子之言。有一是一非也。只是气有以流行言者。有以对待言者。子所引者。以其流行言者也。吾所引者。以其对待言者也。愚请以朱子说證之。语类云阴阳做一个看亦得。做两个看亦得。做两个看。是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做一个看。只是消长。又尝曰阴阳。有对待言者。如夫妇男女东西南北是也。有错综言者。如昼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个间一个辊去是也。又曰。体立天地后。用起天地先。对待底是体。流行底是用。体静而用动。周易本义释易字义曰。卦本伏羲所昼。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又曰。变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对待底。又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四条者。非以流行对待分言一气二气者乎。朱子又释乾卦文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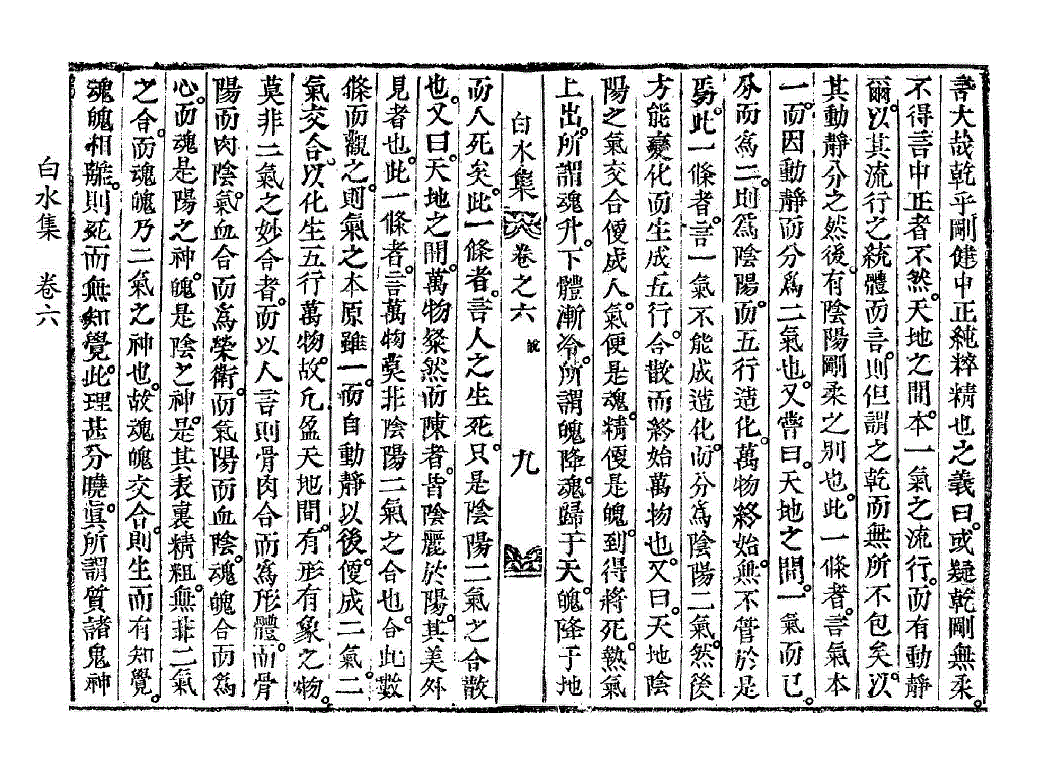 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之义曰。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此一条者。言气本一。而因动静而分为二气也。又尝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终始。无不管于是焉。此一条者。言一气不能成造化。而分为阴阳二气。然后方能变化而生成五行。合散而终始万物也。又曰。天地阴阳之气交合便成人。气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将死。热气上出。所谓魂升。下体渐冷。所谓魄降。魂归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此一条者。言人之生死。只是阴阳二气之合散也。又曰。天地之间。万物粲然而陈者。皆阴丽于阳。其美外见者也。此一条者。言万物莫非阴阳二气之合也。合此数条而观之。则气之本原虽一。而自动静以后。便成二气。二气交合。以化生五行万物。故凡盈天地间。有形有象之物。莫非二气之妙合者。而以人言则骨肉合而为形体。而骨阳而肉阴。气血合而为荣卫。而气阳而血阴。魂魄合而为心。而魂是阳之神。魄是阴之神。是其表里精粗。无非二气之合。而魂魄乃二气之神也。故魂魄交合。则生而有知觉。魂魄相离。则死而无知觉。此理甚分晓。真所谓质诸鬼神
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之义曰。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此一条者。言气本一。而因动静而分为二气也。又尝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终始。无不管于是焉。此一条者。言一气不能成造化。而分为阴阳二气。然后方能变化而生成五行。合散而终始万物也。又曰。天地阴阳之气交合便成人。气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将死。热气上出。所谓魂升。下体渐冷。所谓魄降。魂归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此一条者。言人之生死。只是阴阳二气之合散也。又曰。天地之间。万物粲然而陈者。皆阴丽于阳。其美外见者也。此一条者。言万物莫非阴阳二气之合也。合此数条而观之。则气之本原虽一。而自动静以后。便成二气。二气交合。以化生五行万物。故凡盈天地间。有形有象之物。莫非二气之妙合者。而以人言则骨肉合而为形体。而骨阳而肉阴。气血合而为荣卫。而气阳而血阴。魂魄合而为心。而魂是阳之神。魄是阴之神。是其表里精粗。无非二气之合。而魂魄乃二气之神也。故魂魄交合。则生而有知觉。魂魄相离。则死而无知觉。此理甚分晓。真所谓质诸鬼神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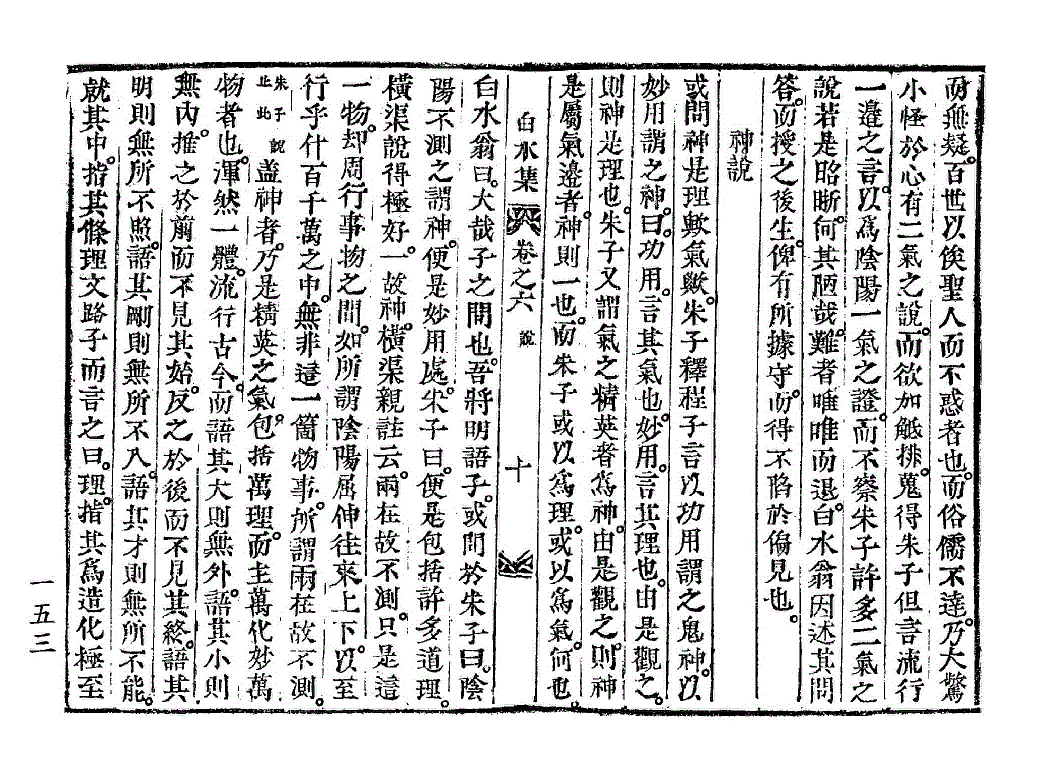 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而俗儒不达。乃大惊小怪于心有二气之说。而欲加抵排。蒐得朱子但言流行一边之言。以为阴阳一气之證。而不察朱子许多二气之说若是昭晢。何其陋哉。难者唯唯而退。白水翁因述其问答。而授之后生。俾有所据守。而得不陷于偏见也。
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而俗儒不达。乃大惊小怪于心有二气之说。而欲加抵排。蒐得朱子但言流行一边之言。以为阴阳一气之證。而不察朱子许多二气之说若是昭晢。何其陋哉。难者唯唯而退。白水翁因述其问答。而授之后生。俾有所据守。而得不陷于偏见也。神说
或问神是理欤气欤。朱子释程子言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曰。功用。言其气也。妙用。言其理也。由是观之。则神是理也。朱子又谓气之精英者为神。由是观之。则神是属气边者。神则一也。而朱子或以为理。或以为气。何也。白水翁曰。大哉子之问也。吾将明语子。或问于朱子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便是妙用处。朱子曰。便是包括许多道理。横渠说得极好。一故神。横渠亲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间。如所谓阴阳屈伸往来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所谓两在故不测。(朱子说止此)盖神者。乃是精英之气。包括万理。而主万化妙万物者也。浑然一体。流行古今。而语其大则无外。语其小则无内。推之于前而不见其始。反之于后而不见其终。语其明则无所不照。语其刚则无所不入。语其才则无所不能。就其中。指其条理文路子而言之曰。理。指其为造化极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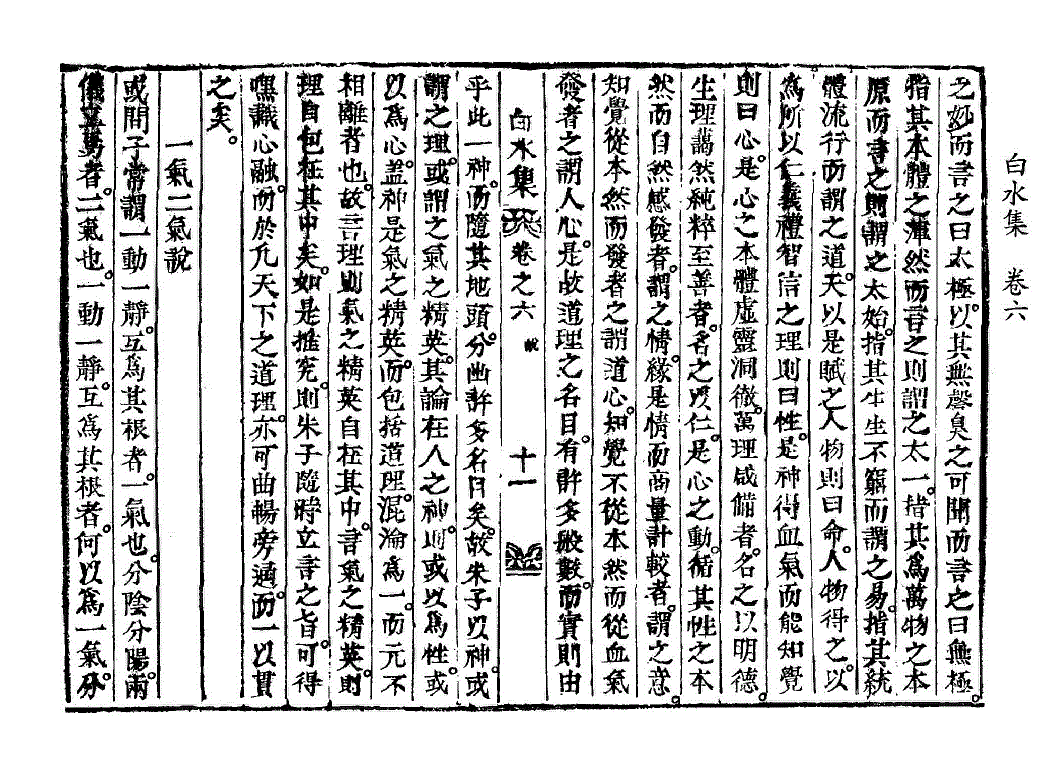 之妙而言之曰太极。以其无声臭之可闻而言之曰无极。指其本体之浑然而言之则谓之太一。指其为万物之本原而言之则谓之太始。指其生生不穷而谓之易。指其统体流行而谓之道。天以是赋之人物则曰命。人物得之。以为所以仁义礼智信之理则曰性。是神得血气而能知觉则曰心。是心之本体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者。名之以明德。生理蔼然纯粹至善者。名之以仁。是心之动。循其性之本然而自然感发者。谓之情。缘是情而商量计较者。谓之意。知觉从本然而发者之谓道心。知觉不从本然而从血气发者之谓人心。是故道理之名目。有许多般数。而实则由乎此一神。而随其地头。分出许多名目矣。故朱子以神。或谓之理。或谓之气之精英。其论在人之神。则或以为性。或以为心。盖神是气之精英。而包括道理。混沦为一。而元不相离者也。故言理则气之精英自在其中。言气之精英。则理自包在其中矣。如是推究。则朱子随时立言之旨。可得嘿识心融。而于凡天下之道理。亦可曲畅旁通。而一以贯之矣。
之妙而言之曰太极。以其无声臭之可闻而言之曰无极。指其本体之浑然而言之则谓之太一。指其为万物之本原而言之则谓之太始。指其生生不穷而谓之易。指其统体流行而谓之道。天以是赋之人物则曰命。人物得之。以为所以仁义礼智信之理则曰性。是神得血气而能知觉则曰心。是心之本体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者。名之以明德。生理蔼然纯粹至善者。名之以仁。是心之动。循其性之本然而自然感发者。谓之情。缘是情而商量计较者。谓之意。知觉从本然而发者之谓道心。知觉不从本然而从血气发者之谓人心。是故道理之名目。有许多般数。而实则由乎此一神。而随其地头。分出许多名目矣。故朱子以神。或谓之理。或谓之气之精英。其论在人之神。则或以为性。或以为心。盖神是气之精英。而包括道理。混沦为一。而元不相离者也。故言理则气之精英自在其中。言气之精英。则理自包在其中矣。如是推究。则朱子随时立言之旨。可得嘿识心融。而于凡天下之道理。亦可曲畅旁通。而一以贯之矣。一气二气说
或问子常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一气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二气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何以为一气。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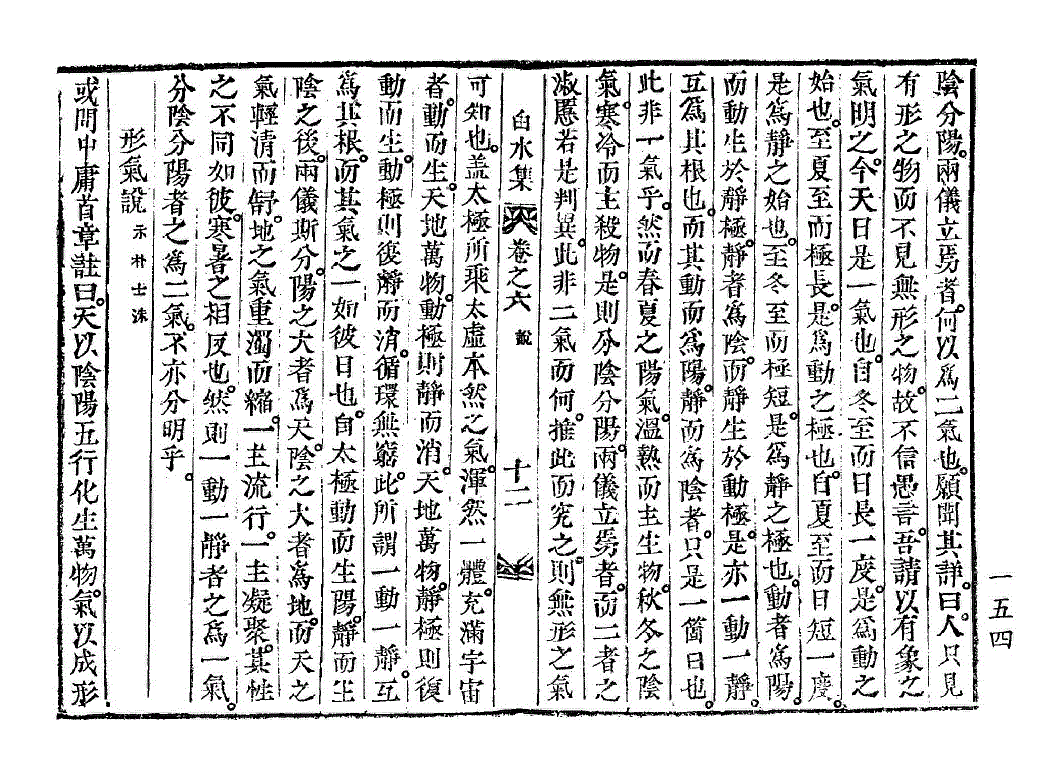 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何以为二气也。愿闻其详。曰。人只见有形之物而不见无形之物。故不信愚言。吾请以有象之气明之。今天日是一气也。自冬至而日长一度。是为动之始也。至夏至而极长。是为动之极也。自夏至而日短一度。是为静之始也。至冬至而极短。是为静之极也。动者为阳。而动生于静极。静者为阴。而静生于动极。是亦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也。而其动而为阳。静而为阴者。只是一个日也。此非一气乎。然而春夏之阳气。温热而主生物。秋冬之阴气。寒冷而主杀物。是则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而二者之淑慝若是判异。此非二气而何。推此而究之。则无形之气可知也。盖太极所乘太虚本然之气。浑然一体。充满宇宙者。动而生。天地万物。动极则静而消。天地万物。静极则复动而生。动极则复静而消。循环无穷。此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而其气之一如彼日也。自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后。两仪斯分。阳之大者为天。阴之大者为地。而天之气轻清而舒。地之气重浊而缩。一主流行。一主凝聚。其性之不同如彼。寒暑之相反也。然则一动一静者之为一气。分阴分阳者之为二气。不亦分明乎。
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何以为二气也。愿闻其详。曰。人只见有形之物而不见无形之物。故不信愚言。吾请以有象之气明之。今天日是一气也。自冬至而日长一度。是为动之始也。至夏至而极长。是为动之极也。自夏至而日短一度。是为静之始也。至冬至而极短。是为静之极也。动者为阳。而动生于静极。静者为阴。而静生于动极。是亦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也。而其动而为阳。静而为阴者。只是一个日也。此非一气乎。然而春夏之阳气。温热而主生物。秋冬之阴气。寒冷而主杀物。是则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而二者之淑慝若是判异。此非二气而何。推此而究之。则无形之气可知也。盖太极所乘太虚本然之气。浑然一体。充满宇宙者。动而生。天地万物。动极则静而消。天地万物。静极则复动而生。动极则复静而消。循环无穷。此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而其气之一如彼日也。自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后。两仪斯分。阳之大者为天。阴之大者为地。而天之气轻清而舒。地之气重浊而缩。一主流行。一主凝聚。其性之不同如彼。寒暑之相反也。然则一动一静者之为一气。分阴分阳者之为二气。不亦分明乎。形气说(示朴士洙)
或问中庸首章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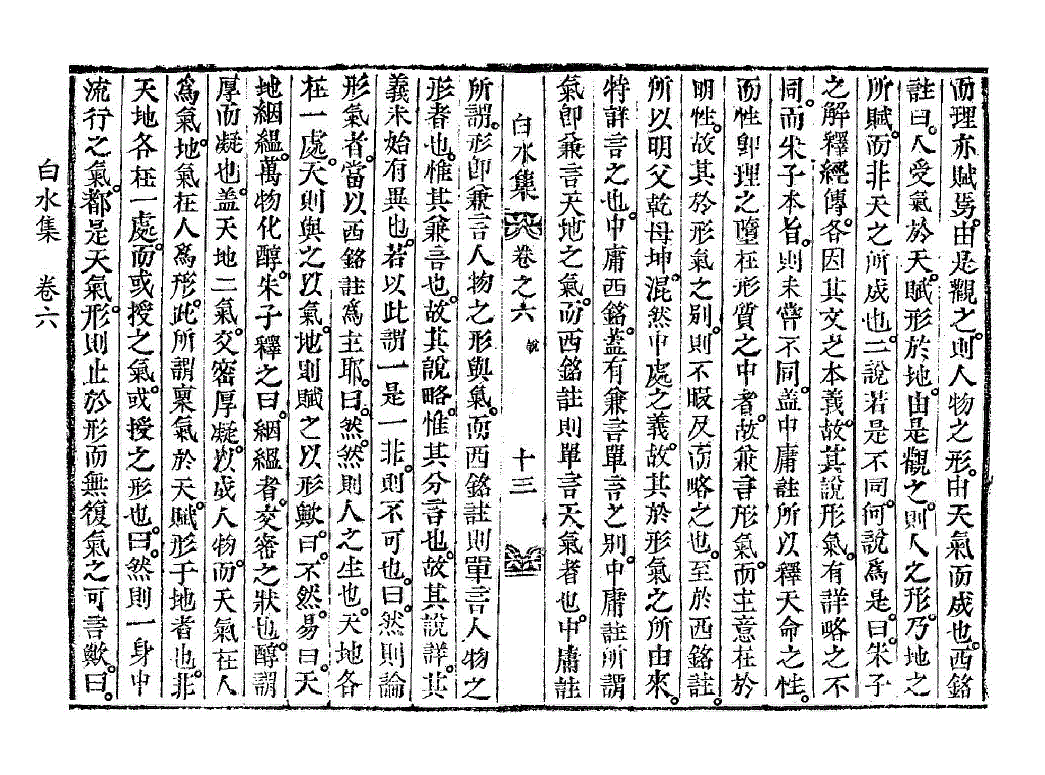 而理亦赋焉。由是观之。则人物之形。由天气而成也。西铭注曰。人受气于天。赋形于地。由是观之。则人之形。乃地之所赋。而非天之所成也。二说若是不同。何说为是。曰。朱子之解释经传。各因其文之本义。故其说形气。有详略之不同。而朱子本旨。则未尝不同。盖中庸注所以释天命之性。而性即理之堕在形质之中者。故兼言形气。而主意在于明性。故其于形气之别。则不暇及而略之也。至于西铭注。所以明父乾母坤。混然中处之义。故其于形气之所由来。特详言之也。中庸西铭。盖有兼言单言之别。中庸注所谓气即兼言天地之气。而西铭注则单言天气者也。中庸注所谓。形即兼言人物之形与气。而西铭注则单言人物之形者也。惟其兼言也。故其说略。惟其分言也。故其说详。其义未始有异也。若以此谓一是一非。则不可也。曰。然则论形气者。当以西铭注为主耶。曰。然。然则人之生也。天地各在一处。天则与之以气。地则赋之以形欤。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朱子释之曰。絪缊者。交密之状也。醇谓厚而凝也。盖天地二气。交密厚凝。以成人物。而天气在人为气。地气在人为形。此所谓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者也。非天地各在一处。而或授之气。或授之形也。曰。然则一身中流行之气。都是天气。形则止于形而无复气之可言欤。曰。
而理亦赋焉。由是观之。则人物之形。由天气而成也。西铭注曰。人受气于天。赋形于地。由是观之。则人之形。乃地之所赋。而非天之所成也。二说若是不同。何说为是。曰。朱子之解释经传。各因其文之本义。故其说形气。有详略之不同。而朱子本旨。则未尝不同。盖中庸注所以释天命之性。而性即理之堕在形质之中者。故兼言形气。而主意在于明性。故其于形气之别。则不暇及而略之也。至于西铭注。所以明父乾母坤。混然中处之义。故其于形气之所由来。特详言之也。中庸西铭。盖有兼言单言之别。中庸注所谓气即兼言天地之气。而西铭注则单言天气者也。中庸注所谓。形即兼言人物之形与气。而西铭注则单言人物之形者也。惟其兼言也。故其说略。惟其分言也。故其说详。其义未始有异也。若以此谓一是一非。则不可也。曰。然则论形气者。当以西铭注为主耶。曰。然。然则人之生也。天地各在一处。天则与之以气。地则赋之以形欤。曰。不然。易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朱子释之曰。絪缊者。交密之状也。醇谓厚而凝也。盖天地二气。交密厚凝。以成人物。而天气在人为气。地气在人为形。此所谓禀气于天。赋形于地者也。非天地各在一处。而或授之气。或授之形也。曰。然则一身中流行之气。都是天气。形则止于形而无复气之可言欤。曰。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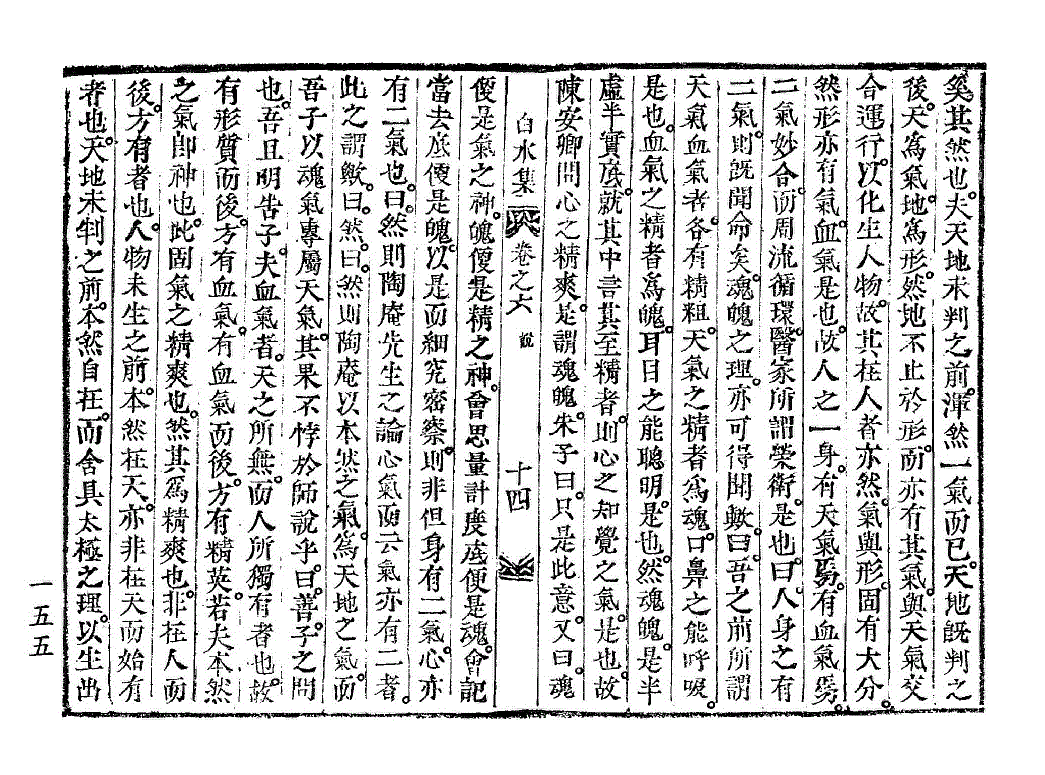 奚其然也。夫天地未判之前。浑然一气而已。天地既判之后。天为气。地为形。然地不止于形。而亦有其气。与天气交合运行。以化生人物。故其在人者亦然。气与形。固有大分。然形亦有气。血气是也。故人之一身。有天气焉。有血气焉。二气妙合。而周流循环。医家所谓荣卫。是也。曰。人身之有二气。则既闻命矣。魂魄之理。亦可得闻欤。曰。吾之前所谓天气血气者。各有精粗。天气之精者为魂。口鼻之能呼吸。是也。血气之精者为魄。耳目之能聪明。是也。然魂魄。是半虚半实底。就其中言其至精者。则心之知觉之气。是也。故陈安卿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朱子曰。只是此意。又曰。魂便是气之神。魄便是精之神。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以是而细究密察。则非但身有二气。心亦有二气也。曰。然则陶庵先生之论心气而云气亦有二者。此之谓欤。曰。然。曰。然则陶庵以本然之气。为天地之气。而吾子以魂气专属天气。其果不悖于师说乎。曰。善。子之问也。吾且明告子。夫血气者。天之所无。而人所独有者也。故有形质而后。方有血气。有血气而后。方有精英。若夫本然之气即神也。此固气之精爽也。然其为精爽也。非在人而后。方有者也。人物未生之前。本然在天。亦非在天而始有者也。天地未判之前。本然自在。而含具太极之理。以生出
奚其然也。夫天地未判之前。浑然一气而已。天地既判之后。天为气。地为形。然地不止于形。而亦有其气。与天气交合运行。以化生人物。故其在人者亦然。气与形。固有大分。然形亦有气。血气是也。故人之一身。有天气焉。有血气焉。二气妙合。而周流循环。医家所谓荣卫。是也。曰。人身之有二气。则既闻命矣。魂魄之理。亦可得闻欤。曰。吾之前所谓天气血气者。各有精粗。天气之精者为魂。口鼻之能呼吸。是也。血气之精者为魄。耳目之能聪明。是也。然魂魄。是半虚半实底。就其中言其至精者。则心之知觉之气。是也。故陈安卿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朱子曰。只是此意。又曰。魂便是气之神。魄便是精之神。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以是而细究密察。则非但身有二气。心亦有二气也。曰。然则陶庵先生之论心气而云气亦有二者。此之谓欤。曰。然。曰。然则陶庵以本然之气。为天地之气。而吾子以魂气专属天气。其果不悖于师说乎。曰。善。子之问也。吾且明告子。夫血气者。天之所无。而人所独有者也。故有形质而后。方有血气。有血气而后。方有精英。若夫本然之气即神也。此固气之精爽也。然其为精爽也。非在人而后。方有者也。人物未生之前。本然在天。亦非在天而始有者也。天地未判之前。本然自在。而含具太极之理。以生出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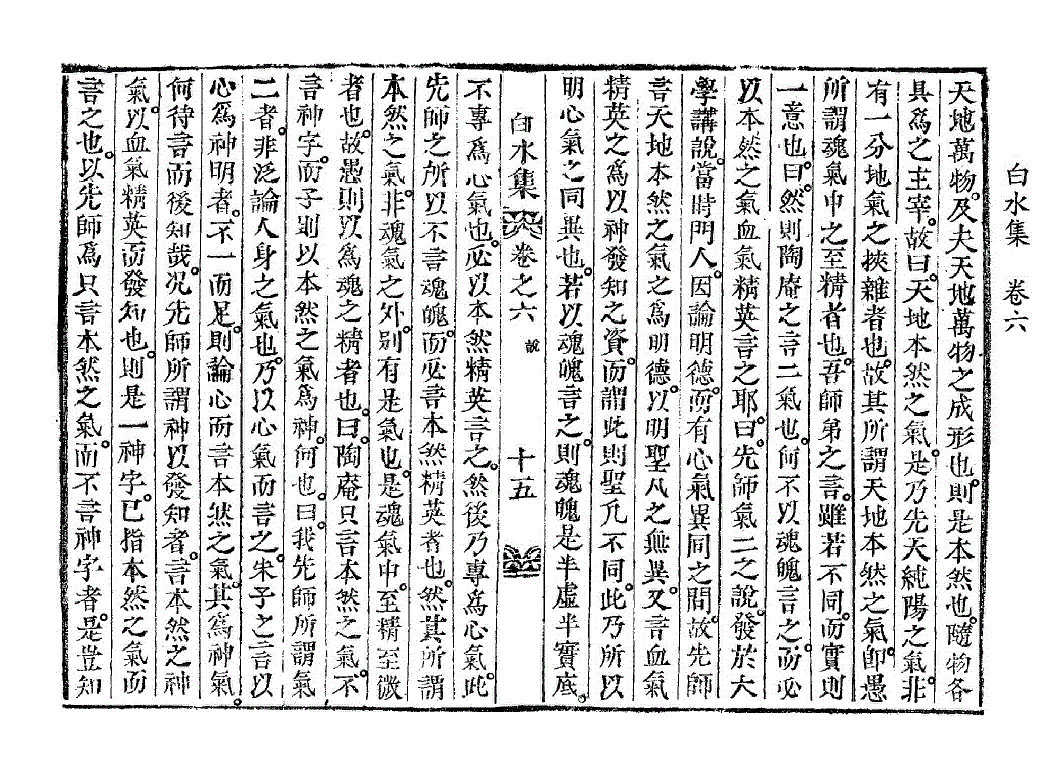 天地万物。及夫天地万物之成形也。则是本然也。随物各具为之主宰。故曰。天地本然之气。是乃先天纯阳之气。非有一分地气之挟杂者也。故其所谓天地本然之气。即愚所谓魂气中之至精者也。吾师弟之言。虽若不同。而实则一意也。曰。然则陶庵之言二气也。何不以魂魄言之。而必以本然之气血气精英言之耶。曰。先师气二之说。发于大学讲说。当时门人。因论明德。而有心气异同之问。故先师言天地本然之气之为明德。以明圣凡之无异。又言血气精英之为以神发知之资。而谓此则圣凡不同。此乃所以明心气之同异也。若以魂魄言之。则魂魄是半虚半实底。不专为心气也。必以本然精英言之。然后乃专为心气。此先师之所以不言魂魄。而必言本然精英者也。然其所谓本然之气。非魂气之外。别有是气也。是魂气中。至精至微者也。故愚则以为魂之精者也。曰。陶庵只言本然之气。不言神字。而子则以本然之气为神。何也。曰。我先师所谓气二者。非泛论人身之气也。乃以心气而言之。朱子之言以心为神明者。不一而足。则论心而言本然之气。其为神气。何待言而后知哉。况先师所谓神以发知者。言本然之神气。以血气精英而发知也。则是一神字。已指本然之气而言之也。以先师为只言本然之气。而不言神字者。是岂知
天地万物。及夫天地万物之成形也。则是本然也。随物各具为之主宰。故曰。天地本然之气。是乃先天纯阳之气。非有一分地气之挟杂者也。故其所谓天地本然之气。即愚所谓魂气中之至精者也。吾师弟之言。虽若不同。而实则一意也。曰。然则陶庵之言二气也。何不以魂魄言之。而必以本然之气血气精英言之耶。曰。先师气二之说。发于大学讲说。当时门人。因论明德。而有心气异同之问。故先师言天地本然之气之为明德。以明圣凡之无异。又言血气精英之为以神发知之资。而谓此则圣凡不同。此乃所以明心气之同异也。若以魂魄言之。则魂魄是半虚半实底。不专为心气也。必以本然精英言之。然后乃专为心气。此先师之所以不言魂魄。而必言本然精英者也。然其所谓本然之气。非魂气之外。别有是气也。是魂气中。至精至微者也。故愚则以为魂之精者也。曰。陶庵只言本然之气。不言神字。而子则以本然之气为神。何也。曰。我先师所谓气二者。非泛论人身之气也。乃以心气而言之。朱子之言以心为神明者。不一而足。则论心而言本然之气。其为神气。何待言而后知哉。况先师所谓神以发知者。言本然之神气。以血气精英而发知也。则是一神字。已指本然之气而言之也。以先师为只言本然之气。而不言神字者。是岂知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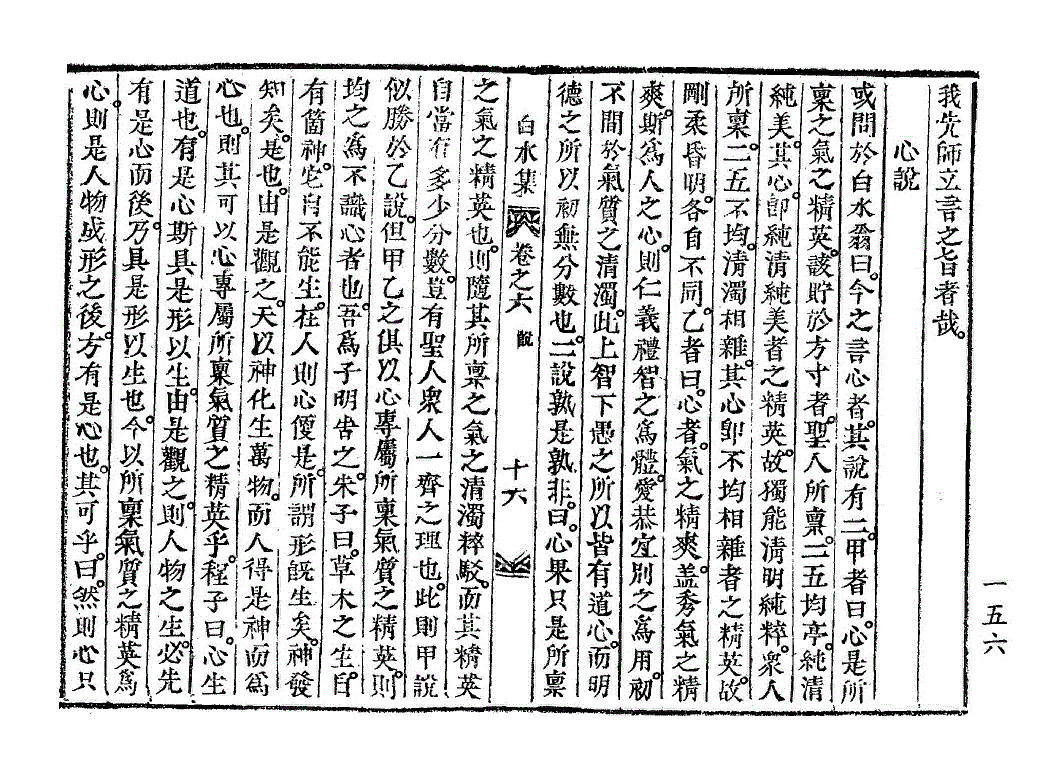 我先师立言之旨者哉。
我先师立言之旨者哉。心说
或问于白水翁曰。今之言心者。其说有二。甲者曰。心是所禀之气之精英。该贮于方寸者。圣人所禀。二五均亭。纯清纯美。其心。即纯清纯美者之精英。故独能清明纯粹。众人所禀。二五不均。清浊相杂。其心即不均相杂者之精英。故刚柔昏明。各自不同。乙者曰。心者。气之精爽。盖秀气之精爽。斯为人之心。则仁义礼智之为体。爱恭宜别之为用。初不间于气质之清浊。此上智下愚之所以皆有道心。而明德之所以初无分数也。二说孰是孰非。曰。心果只是所禀之气之精英也。则随其所禀之气之清浊粹驳。而其精英自当有多少分数。岂有圣人众人一齐之理也。此则甲说似胜于乙说。但甲乙之俱以心专属所禀气质之精英。则均之为不识心者也。吾为子明告之。朱子曰。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则心便是。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是也。由是观之。天以神化生万物。而人得是神而为心也。则其可以心专属所禀气质之精英乎。程子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由是观之。则人物之生。必先有是心而后。乃具是形以生也。今以所禀气质之精英为心。则是人物成形之后。方有是心也。其可乎。曰。然则心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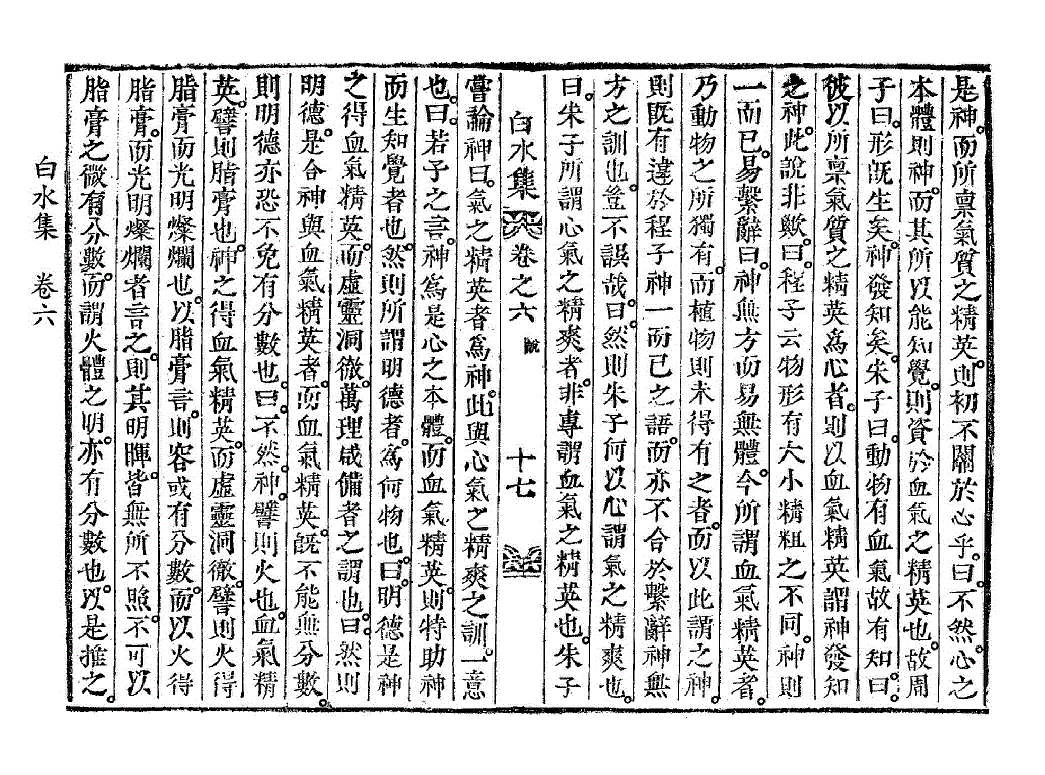 是神。而所禀气质之精英。则初不关于心乎。曰。不然。心之本体则神。而其所以能知觉。则资于血气之精英也。故周子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朱子曰。动物有血气故有知。曰。彼以所禀气质之精英为心者。则以血气精英谓神发知之神。此说非欤。曰。程子云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则一而已。易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今所谓血气精英者。乃动物之所独有。而植物则未得有之者。而以此谓之神。则既有违于程子神一而已之语。而亦不合于系辞神无方之训也。岂不误哉。曰。然则朱子何以心谓气之精爽也。曰。朱子所谓心气之精爽者。非专谓血气之精英也。朱子尝论神曰。气之精英者为神。此与心气之精爽之训。一意也。曰。若子之言。神为是心之本体。而血气精英。则特助神而生知觉者也。然则所谓明德者。为何物也。曰。明德是神之得血气精英。而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者之谓也。曰。然则明德。是合神与血气精英者。而血气精英。既不能无分数。则明德亦恐不免有分数也。曰。不然。神。譬则火也。血气精英。譬则脂膏也。神之得血气精英。而虚灵洞彻。譬则火得脂膏而光明灿烂也。以脂膏言。则容或有分数。而以火得脂膏。而光明灿烂者言之。则其明晖。皆无所不照。不可以脂膏之微有分数。而谓火体之明。亦有分数也。以是推之。
是神。而所禀气质之精英。则初不关于心乎。曰。不然。心之本体则神。而其所以能知觉。则资于血气之精英也。故周子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朱子曰。动物有血气故有知。曰。彼以所禀气质之精英为心者。则以血气精英谓神发知之神。此说非欤。曰。程子云物形有大小精粗之不同。神则一而已。易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今所谓血气精英者。乃动物之所独有。而植物则未得有之者。而以此谓之神。则既有违于程子神一而已之语。而亦不合于系辞神无方之训也。岂不误哉。曰。然则朱子何以心谓气之精爽也。曰。朱子所谓心气之精爽者。非专谓血气之精英也。朱子尝论神曰。气之精英者为神。此与心气之精爽之训。一意也。曰。若子之言。神为是心之本体。而血气精英。则特助神而生知觉者也。然则所谓明德者。为何物也。曰。明德是神之得血气精英。而虚灵洞彻。万理咸备者之谓也。曰。然则明德。是合神与血气精英者。而血气精英。既不能无分数。则明德亦恐不免有分数也。曰。不然。神。譬则火也。血气精英。譬则脂膏也。神之得血气精英。而虚灵洞彻。譬则火得脂膏而光明灿烂也。以脂膏言。则容或有分数。而以火得脂膏。而光明灿烂者言之。则其明晖。皆无所不照。不可以脂膏之微有分数。而谓火体之明。亦有分数也。以是推之。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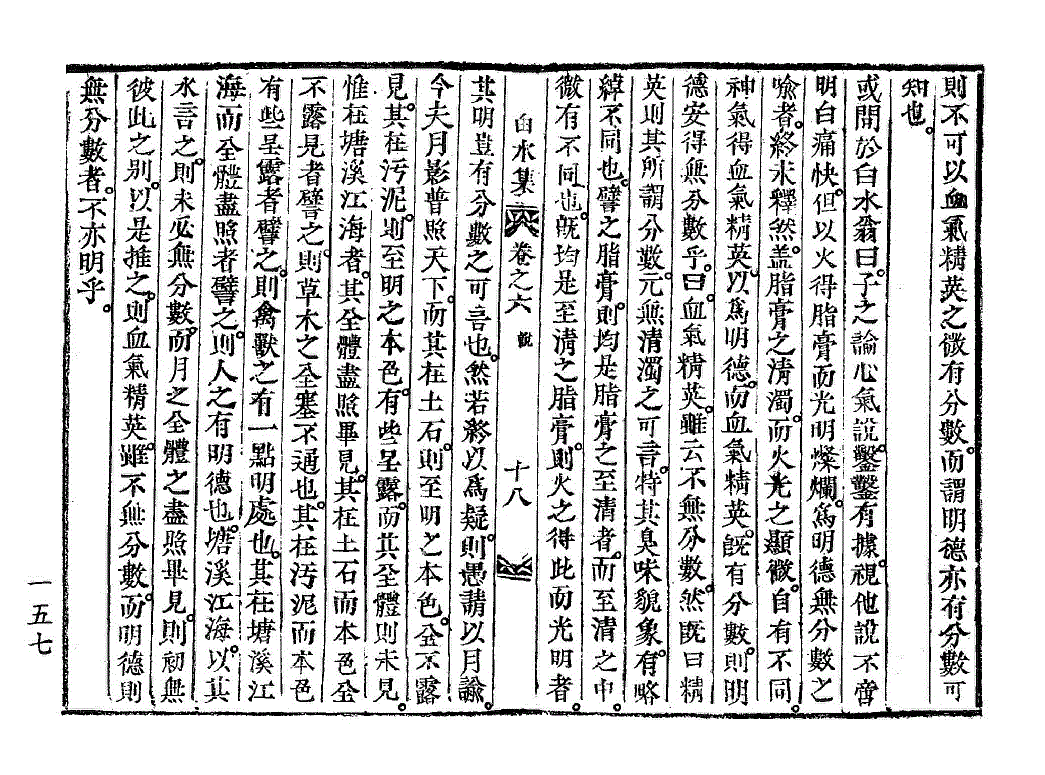 则不可以血气精英之微有分数。而谓明德亦有分数可知也。
则不可以血气精英之微有分数。而谓明德亦有分数可知也。或问于白水翁曰。子之论心气说。凿凿有据。视他说不啻明白痛快。但以火得脂膏而光明灿烂。为明德无分数之喻者。终未释然。盖脂膏之清浊。而火光之显微。自有不同。神气得血气精英。以为明德。而血气精英。既有分数。则明德安得无分数乎。曰。血气精英。虽云不无分数。然既曰精英则其所谓分数。元无清浊之可言。特其臭味貌象。有略绰不同也。譬之脂膏。则均是脂膏之至清者。而至清之中。微有不同也。既均是至清之脂膏。则火之得此而光明者。其明岂有分数之可言也。然若终以为疑。则愚请以月谕。今夫月影普照天下。而其在土石。则至明之本色。全不露见。其在污泥。则至明之本色。有些呈露。而其全体则未见。惟在塘溪江海者。其全体尽照毕见。其在土石而本色全不露见者譬之。则草木之全塞不通也。其在污泥而本色有些呈露者譬之。则禽兽之有一点明处也。其在塘溪江海而全体尽照者譬之。则人之有明德也。塘溪江海。以其水言之。则未必无分数。而月之全体之尽照毕见。则初无彼此之别。以是推之。则血气精英。虽不无分数。而明德则无分数者。不亦明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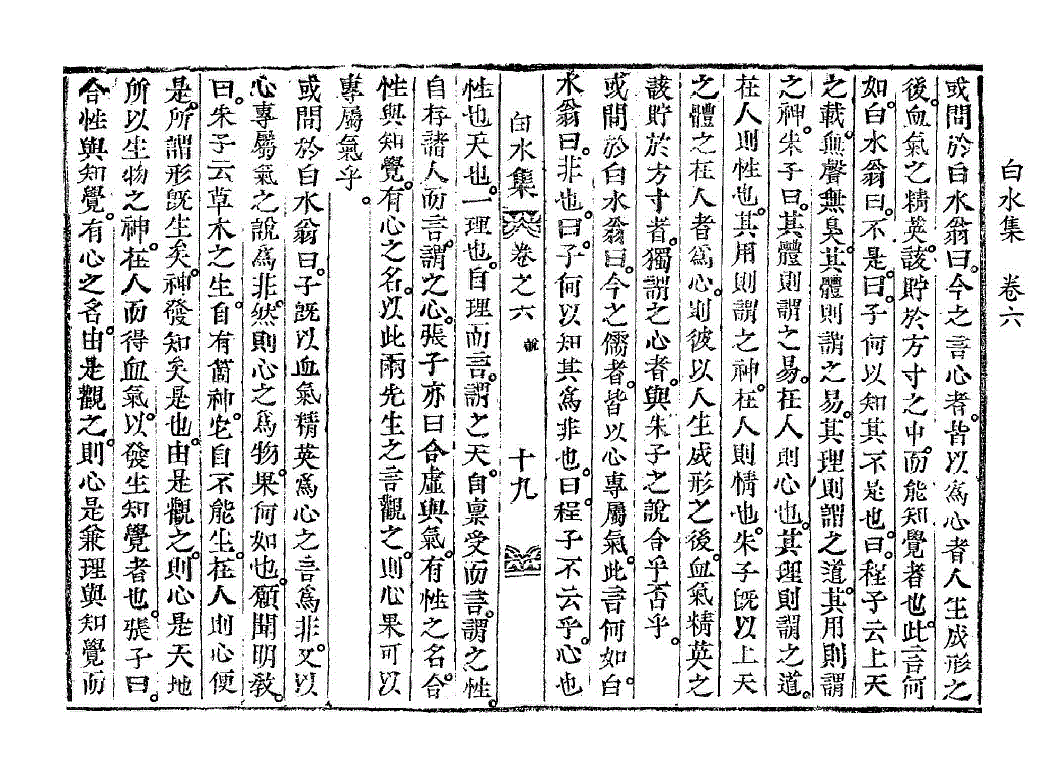 或问于白水翁曰。今之言心者。皆以为心者人生成形之后。血气之精英。该贮于方寸之中。而能知觉者也。此言何如。白水翁曰。不是。曰。子何以知其不是也。曰。程子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朱子既以上天之体之在人者为心。则彼以人生成形之后。血气精英之该贮于方寸者。独谓之心者。与朱子之说合乎否乎。
或问于白水翁曰。今之言心者。皆以为心者人生成形之后。血气之精英。该贮于方寸之中。而能知觉者也。此言何如。白水翁曰。不是。曰。子何以知其不是也。曰。程子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朱子既以上天之体之在人者为心。则彼以人生成形之后。血气精英之该贮于方寸者。独谓之心者。与朱子之说合乎否乎。或问于白水翁曰。今之儒者。皆以心专属气。此言何如。白水翁曰。非也。曰。子何以知其为非也。曰。程子不云乎。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张子亦曰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以此两先生之言观之。则心果可以专属气乎。
或问于白水翁曰。子既以血气精英为心之言为非。又以心专属气之说为非。然则心之为物。果何如也。愿闻明教。曰。朱子云草木之生。自有个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则心便是。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是也。由是观之。则心是天地所以生物之神。在人而得血气。以发生知觉者也。张子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由是观之。则心是兼理与知觉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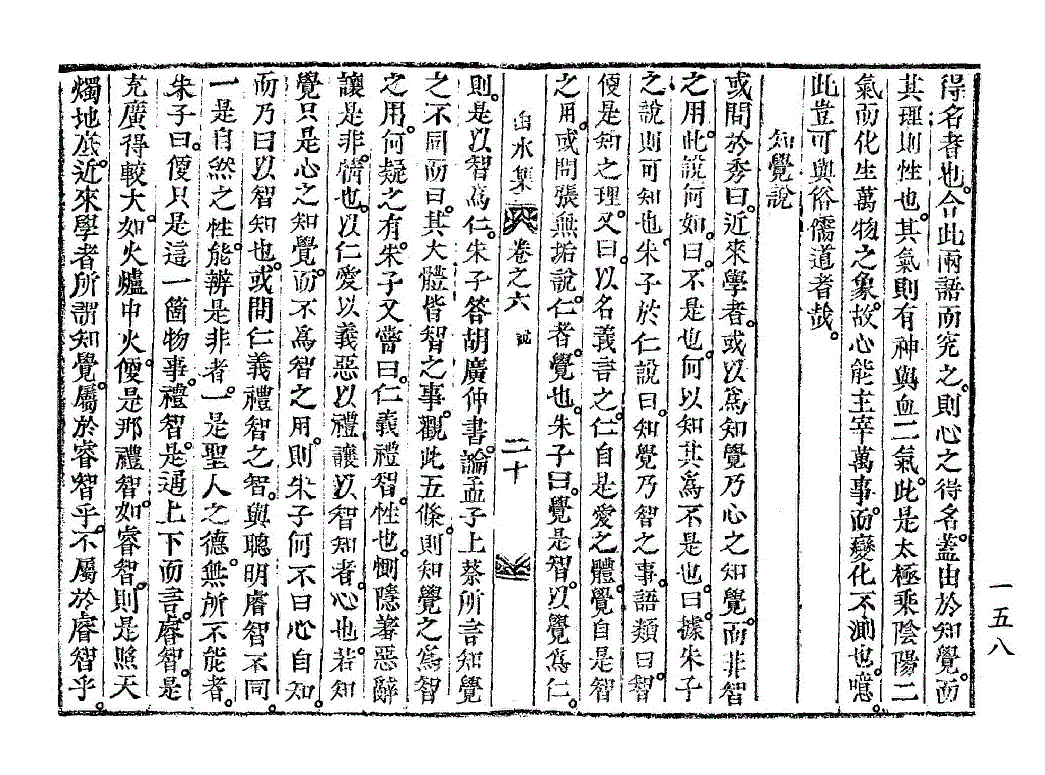 得名者也。合此两语而究之。则心之得名。盖由于知觉。而其理则性也。其气则有神与血二气。此是太极乘阴阳二气而化生万物之象。故心能主宰万事。而变化不测也。噫。此岂可与俗儒道者哉。
得名者也。合此两语而究之。则心之得名。盖由于知觉。而其理则性也。其气则有神与血二气。此是太极乘阴阳二气而化生万物之象。故心能主宰万事。而变化不测也。噫。此岂可与俗儒道者哉。知觉说
或问于秀曰。近来学者。或以为知觉乃心之知觉。而非智之用。此说何如。曰。不是也。何以知其为不是也。曰。据朱子之说则可知也。朱子于仁说曰。知觉乃智之事。语类曰。智便是知之理。又曰。以名义言之。仁自是爱之体。觉自是智之用。或问张无垢说。仁者。觉也。朱子曰。觉是智。以觉为仁。则。是以智为仁。朱子答胡广仲书。论孟子上蔡所言知觉之不同而曰。其大体皆智之事。观此五条。则知觉之为智之用。何疑之有。朱子又尝曰。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若知觉只是心之知觉。而不为智之用。则朱子何不曰心自知。而乃曰以智知也。或问仁义礼智之智。与聪明睿智不同。一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一是圣人之德。无所不能者。朱子曰。便只是这一个物事。礼智。是通上下而言。睿智。是充广得较大。如火炉中火。便是那礼智。如睿智。则是照天烛地底。近来学者所谓知觉。属于睿智乎。不属于睿智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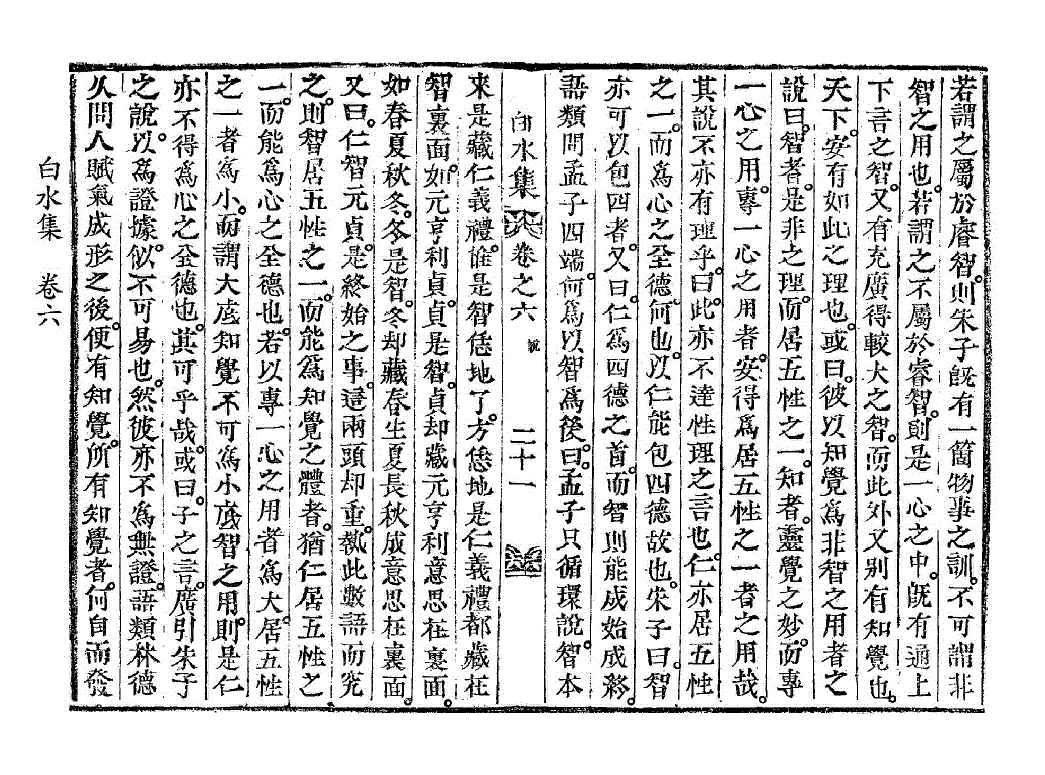 若谓之属于睿智。则朱子既有一个物事之训。不可谓非智之用也。若谓之不属于睿智。则是一心之中。既有通上下言之智。又有充广得较大之智。而此外又别有知觉也。天下。安有如此之理也。或曰。彼以知觉为非智之用者之说曰。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灵觉之妙。而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用者。安得为居五性之一者之用哉。其说不亦有理乎。曰。此亦不达性理之言也。仁亦居五性之一。而为心之全德。何也。以仁能包四德故也。朱子曰。智亦可以包四者。又曰。仁为四德之首。而智则能成始成终。语类问孟子四端。何为以智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智恁地了。方恁地是仁义礼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又曰。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执此数语而究之。则智居五性之一。而能为知觉之体者。犹仁居五性之一。而能为心之全德也。若以专一心之用者为大。居五性之一者为小。而谓大底知觉不可为小底智之用。则是仁亦不得为心之全德也。其可乎哉。或曰。子之言。广引朱子之说。以为證据。似不可易也。然彼亦不为无證。语类林德久问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所有知觉者。何自而发
若谓之属于睿智。则朱子既有一个物事之训。不可谓非智之用也。若谓之不属于睿智。则是一心之中。既有通上下言之智。又有充广得较大之智。而此外又别有知觉也。天下。安有如此之理也。或曰。彼以知觉为非智之用者之说曰。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灵觉之妙。而专一心之用。专一心之用者。安得为居五性之一者之用哉。其说不亦有理乎。曰。此亦不达性理之言也。仁亦居五性之一。而为心之全德。何也。以仁能包四德故也。朱子曰。智亦可以包四者。又曰。仁为四德之首。而智则能成始成终。语类问孟子四端。何为以智为后。曰。孟子只循环说。智本来是藏仁义礼。惟是智恁地了。方恁地是仁义礼都藏在智里面。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如春夏秋冬。冬是智。冬却藏春生夏长秋成意思在里面。又曰。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执此数语而究之。则智居五性之一。而能为知觉之体者。犹仁居五性之一。而能为心之全德也。若以专一心之用者为大。居五性之一者为小。而谓大底知觉不可为小底智之用。则是仁亦不得为心之全德也。其可乎哉。或曰。子之言。广引朱子之说。以为證据。似不可易也。然彼亦不为无證。语类林德久问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所有知觉者。何自而发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5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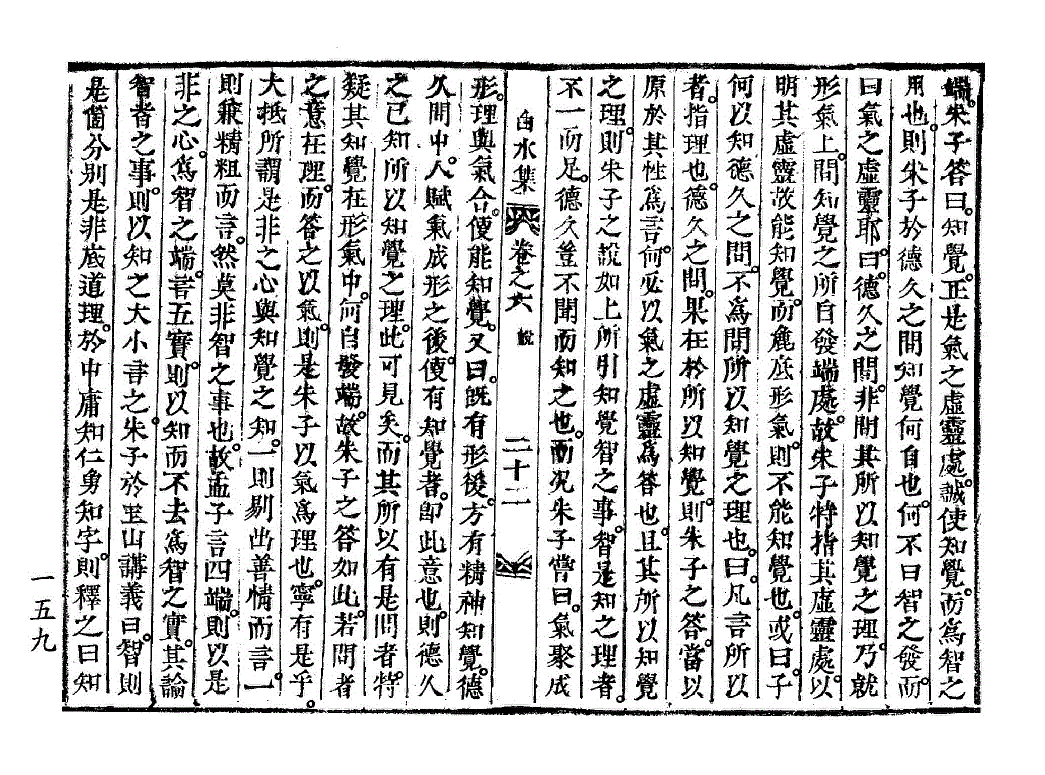 端。朱子答曰。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诚使知觉。而为智之用也。则朱子于德久之问知觉何自也。何不曰智之发。而曰气之虚灵耶。曰。德久之问。非问其所以知觉之理。乃就形气上。问知觉之所自发端处。故朱子特指其虚灵处。以明其虚灵故能知觉。而粗底形气。则不能知觉也。或曰。子何以知德久之问。不为问所以知觉之理也。曰。凡言所以者。指理也。德久之问。果在于所以知觉。则朱子之答。当以原于其性为言。何必以气之虚灵为答也。且其所以知觉之理。则朱子之说如上所引知觉智之事。智是知之理者。不一而足。德久岂不闻而知之也。而况朱子尝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又曰。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德久问中。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者。即此意也。则德久之已知所以知觉之理。此可见矣。而其所以有是问者。特疑其知觉在形气中。何自发端。故朱子之答如此。若问者之意在理。而答之以气。则是朱子以气为理也。宁有是乎。大抵所谓是非之心与知觉之知。一则剔出善情而言。一则兼精粗而言。然莫非智之事也。故孟子言四端。则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言五实。则以知而不去为智之实。其论智者之事。则以知之大小言之。朱子于玉山讲义曰。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于中庸知仁勇知字。则释之曰知
端。朱子答曰。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诚使知觉。而为智之用也。则朱子于德久之问知觉何自也。何不曰智之发。而曰气之虚灵耶。曰。德久之问。非问其所以知觉之理。乃就形气上。问知觉之所自发端处。故朱子特指其虚灵处。以明其虚灵故能知觉。而粗底形气。则不能知觉也。或曰。子何以知德久之问。不为问所以知觉之理也。曰。凡言所以者。指理也。德久之问。果在于所以知觉。则朱子之答。当以原于其性为言。何必以气之虚灵为答也。且其所以知觉之理。则朱子之说如上所引知觉智之事。智是知之理者。不一而足。德久岂不闻而知之也。而况朱子尝曰。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又曰。既有形后。方有精神知觉。德久问中。人赋气成形之后。便有知觉者。即此意也。则德久之已知所以知觉之理。此可见矣。而其所以有是问者。特疑其知觉在形气中。何自发端。故朱子之答如此。若问者之意在理。而答之以气。则是朱子以气为理也。宁有是乎。大抵所谓是非之心与知觉之知。一则剔出善情而言。一则兼精粗而言。然莫非智之事也。故孟子言四端。则以是非之心。为智之端。言五实。则以知而不去为智之实。其论智者之事。则以知之大小言之。朱子于玉山讲义曰。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于中庸知仁勇知字。则释之曰知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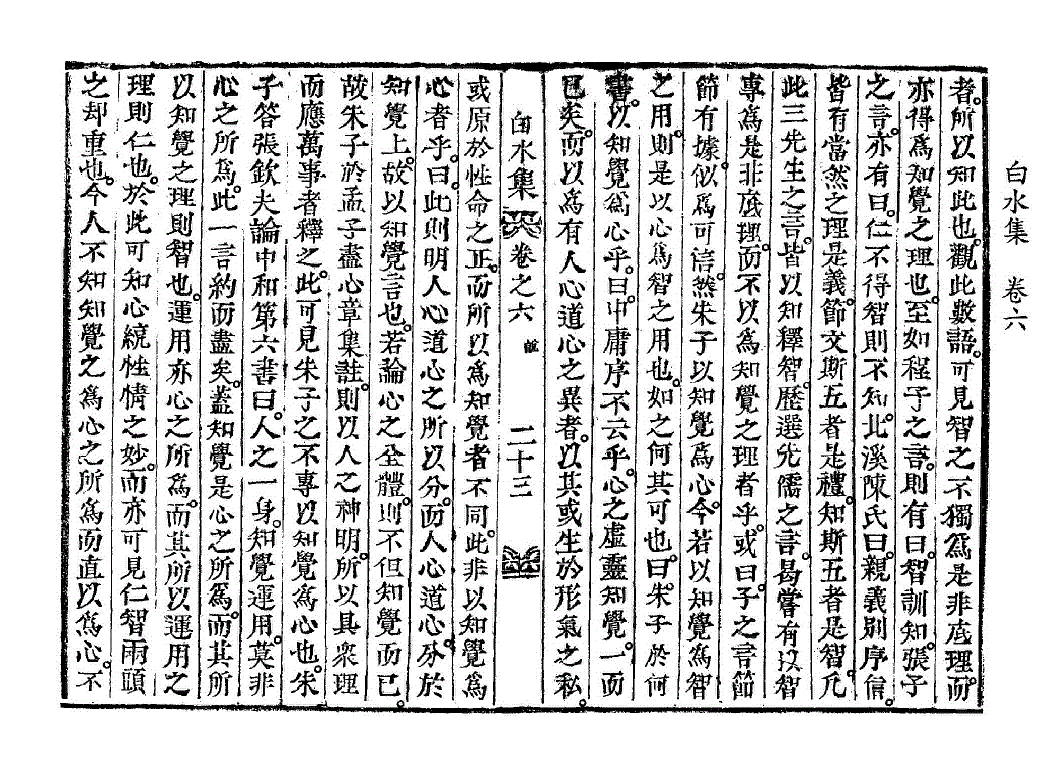 者。所以知此也。观此数语。可见智之不独为是非底理。而亦得为知觉之理也。至如程子之言。则有曰。智训知。张子之言。亦有曰。仁不得智则不知。北溪陈氏曰。亲义别序信。皆有当然之理是义。节文斯五者是礼。知斯五者是智。凡此三先生之言。皆以知释智。历选先儒之言。曷尝有以智专为是非底理。而不以为知觉之理者乎。或曰。子之言节节有据。似为可信。然朱子以知觉为心。今若以知觉为智之用。则是以心为智之用也。如之何其可也。曰。朱子于何书。以知觉为心乎。曰。中庸序不云乎。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此非以知觉为心者乎。曰。此则明人心道心之所以分。而人心道心。分于知觉上。故以知觉言也。若论心之全体。则不但知觉而已。故朱子于孟子尽心章集注。则以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释之。此可见朱子之不专以知觉为心也。朱子答张钦夫论中和第六书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此一言约而尽矣。盖知觉是心之所为。而其所以知觉之理则智也。运用亦心之所为。而其所以运用之理则仁也。于此可知心统性情之妙。而亦可见仁智两头之却重也。今人不知知觉之为心之所为而直以为心。不
者。所以知此也。观此数语。可见智之不独为是非底理。而亦得为知觉之理也。至如程子之言。则有曰。智训知。张子之言。亦有曰。仁不得智则不知。北溪陈氏曰。亲义别序信。皆有当然之理是义。节文斯五者是礼。知斯五者是智。凡此三先生之言。皆以知释智。历选先儒之言。曷尝有以智专为是非底理。而不以为知觉之理者乎。或曰。子之言节节有据。似为可信。然朱子以知觉为心。今若以知觉为智之用。则是以心为智之用也。如之何其可也。曰。朱子于何书。以知觉为心乎。曰。中庸序不云乎。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此非以知觉为心者乎。曰。此则明人心道心之所以分。而人心道心。分于知觉上。故以知觉言也。若论心之全体。则不但知觉而已。故朱子于孟子尽心章集注。则以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释之。此可见朱子之不专以知觉为心也。朱子答张钦夫论中和第六书曰。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此一言约而尽矣。盖知觉是心之所为。而其所以知觉之理则智也。运用亦心之所为。而其所以运用之理则仁也。于此可知心统性情之妙。而亦可见仁智两头之却重也。今人不知知觉之为心之所为而直以为心。不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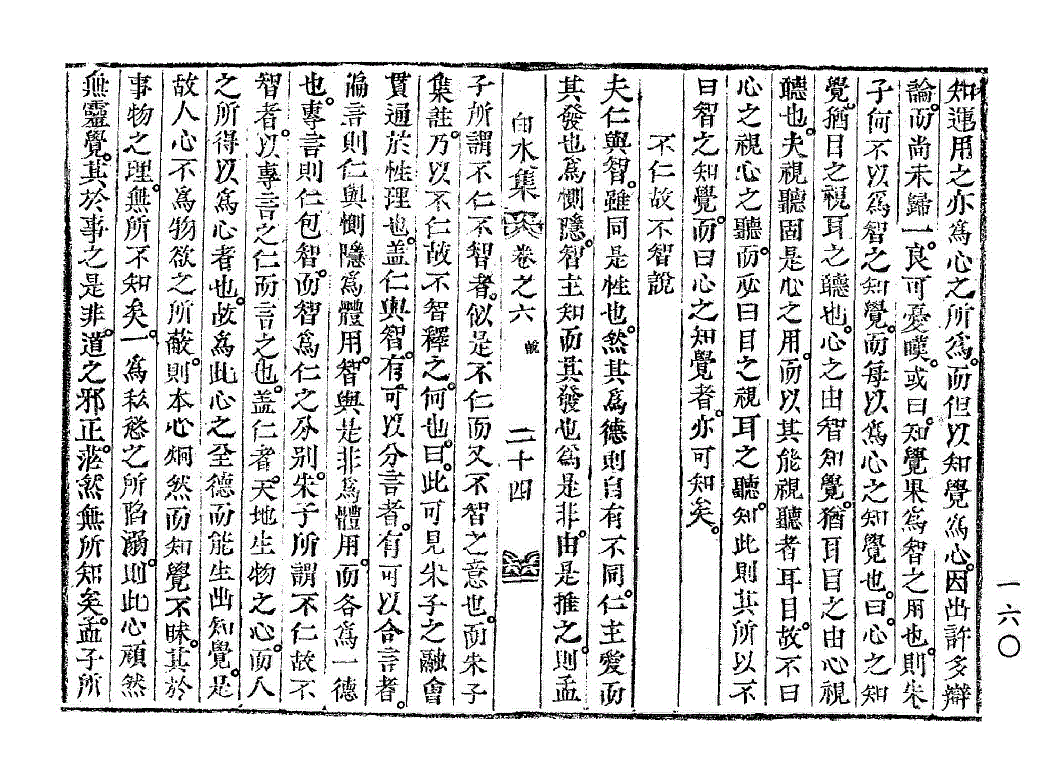 知运用之亦为心之所为。而但以知觉为心。因出许多辩论。而尚未归一。良可忧叹。或曰。知觉果为智之用也。则朱子何不以为智之知觉。而每以为心之知觉也。曰。心之知觉。犹目之视耳之听也。心之由智知觉。犹耳目之由心视听也。夫视听固是心之用。而以其能视听者耳目。故不曰心之视心之听。而必曰目之视耳之听。知此则其所以不曰智之知觉。而曰心之知觉者。亦可知矣。
知运用之亦为心之所为。而但以知觉为心。因出许多辩论。而尚未归一。良可忧叹。或曰。知觉果为智之用也。则朱子何不以为智之知觉。而每以为心之知觉也。曰。心之知觉。犹目之视耳之听也。心之由智知觉。犹耳目之由心视听也。夫视听固是心之用。而以其能视听者耳目。故不曰心之视心之听。而必曰目之视耳之听。知此则其所以不曰智之知觉。而曰心之知觉者。亦可知矣。不仁故不智说
夫仁与智。虽同是性也。然其为德则自有不同。仁主爱而其发也为恻隐。智主知而其发也为是非。由是推之。则孟子所谓不仁不智者。似是不仁而又不智之意也。而朱子集注。乃以不仁故不智释之。何也。曰。此可见朱子之融会贯通于性理也。盖仁与智。有可以分言者。有可以合言者。偏言则仁与恻隐为体用。智与是非为体用。而各为一德也。专言则仁包智。而智为仁之分别。朱子所谓不仁故不智者。以专言之仁而言之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故为此心之全德而能生出知觉。是故人心不为物欲之所蔽。则本心炯然而知觉不昧。其于事物之理。无所不知矣。一为私欲之所陷溺。则此心顽然无灵觉。其于事之是非。道之邪正。茫然无所知矣。孟子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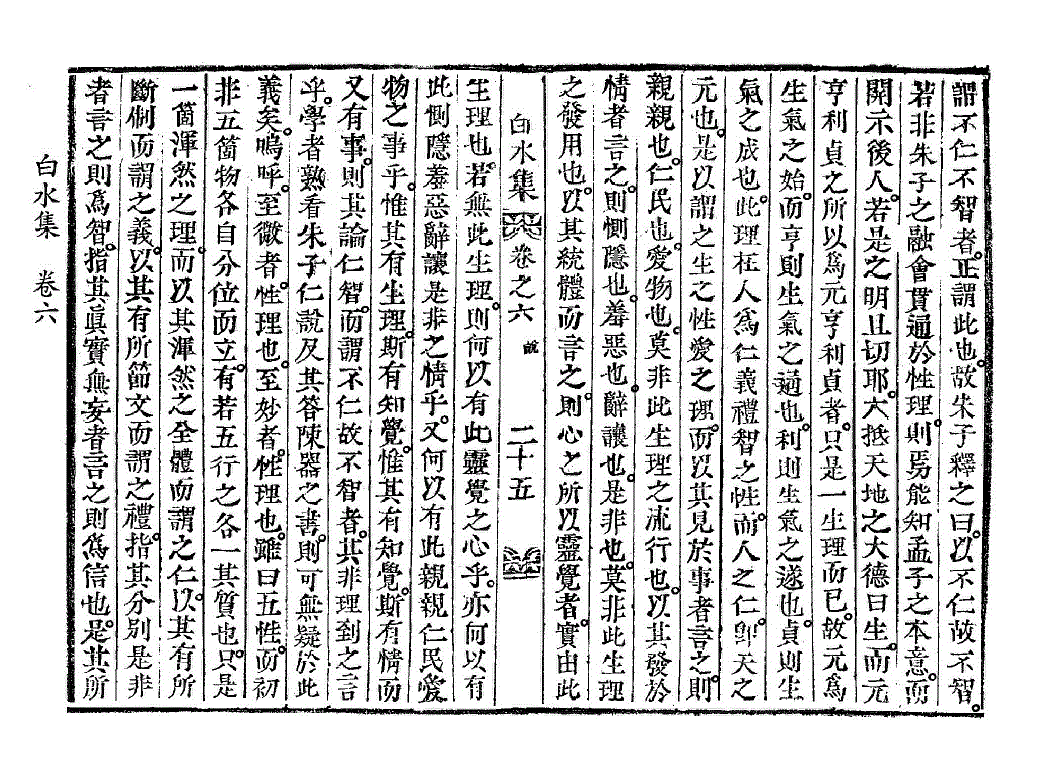 谓不仁不智者。正谓此也。故朱子释之曰。以不仁故不智。若非朱子之融会贯通于性理。则焉能知孟子之本意。而开示后人。若是之明且切耶。大抵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元亨利贞之所以为元亨利贞者。只是一生理而已。故元为生气之始。而亨则生气之通也。利则生气之遂也。贞则生气之成也。此理在人为仁义礼智之性。而人之仁。即天之元也。是以谓之生之性爱之理。而以其见于事者言之。则亲亲也。仁民也。爱物也。莫非此生理之流行也。以其发于情者言之。则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莫非此生理之发用也。以其统体而言之。则心之所以灵觉者。实由此生理也。若无此生理。则何以有此灵觉之心乎。亦何以有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乎。又何以有此亲亲仁民爱物之事乎。惟其有生理。斯有知觉。惟其有知觉。斯有情而又有事。则其论仁智。而谓不仁故不智者。其非理到之言乎。学者熟看朱子仁说及其答陈器之书。则可无疑于此义矣。呜呼。至微者。性理也。至妙者。性理也。虽曰五性。而初非五个物各自分位而立。有若五行之各一其质也。只是一个浑然之理。而以其浑然之全体而谓之仁。以其有所断制而谓之义。以其有所节文而谓之礼。指其分别是非者言之则为智。指其真实无妄者言之则为信也。是其所
谓不仁不智者。正谓此也。故朱子释之曰。以不仁故不智。若非朱子之融会贯通于性理。则焉能知孟子之本意。而开示后人。若是之明且切耶。大抵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元亨利贞之所以为元亨利贞者。只是一生理而已。故元为生气之始。而亨则生气之通也。利则生气之遂也。贞则生气之成也。此理在人为仁义礼智之性。而人之仁。即天之元也。是以谓之生之性爱之理。而以其见于事者言之。则亲亲也。仁民也。爱物也。莫非此生理之流行也。以其发于情者言之。则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莫非此生理之发用也。以其统体而言之。则心之所以灵觉者。实由此生理也。若无此生理。则何以有此灵觉之心乎。亦何以有此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乎。又何以有此亲亲仁民爱物之事乎。惟其有生理。斯有知觉。惟其有知觉。斯有情而又有事。则其论仁智。而谓不仁故不智者。其非理到之言乎。学者熟看朱子仁说及其答陈器之书。则可无疑于此义矣。呜呼。至微者。性理也。至妙者。性理也。虽曰五性。而初非五个物各自分位而立。有若五行之各一其质也。只是一个浑然之理。而以其浑然之全体而谓之仁。以其有所断制而谓之义。以其有所节文而谓之礼。指其分别是非者言之则为智。指其真实无妄者言之则为信也。是其所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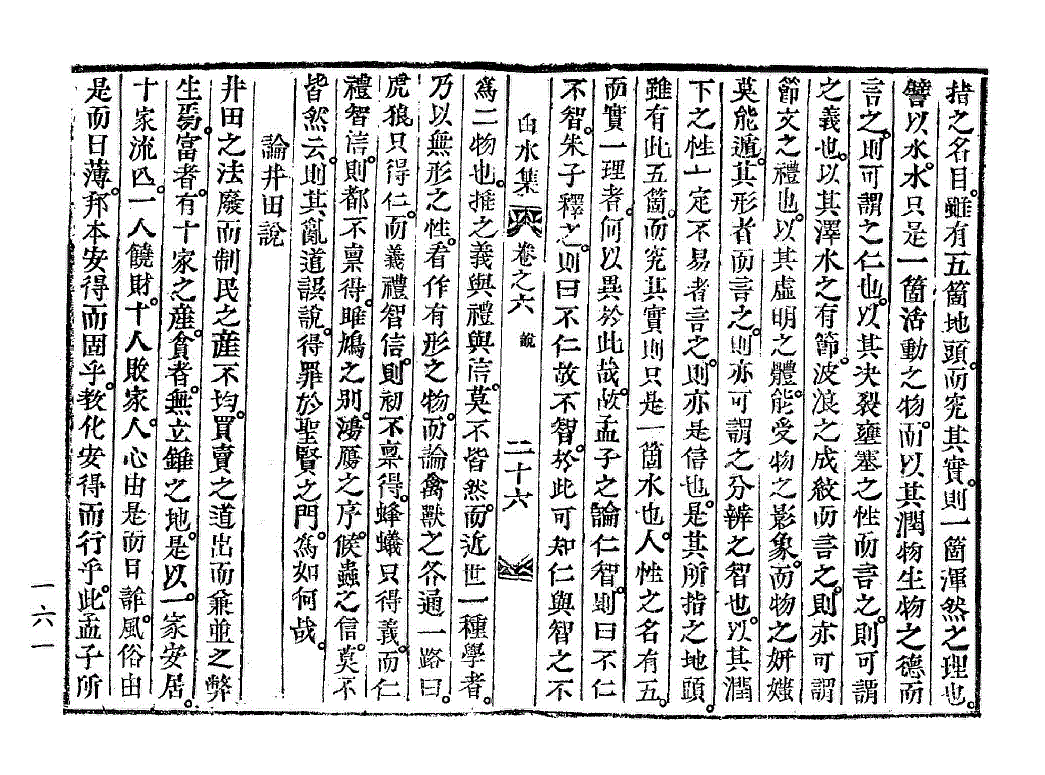 指之名目。虽有五个地头。而究其实。则一个浑然之理也。譬以水。水只是一个活动之物。而以其润物生物之德而言之。则可谓之仁也。以其决裂壅塞之性而言之。则可谓之义也。以其泽水之有节。波浪之成纹而言之。则亦可谓节文之礼也。以其虚明之体。能受物之影象。而物之妍媸莫能遁。其形者而言之。则亦可谓之分辨之智也。以其润下之性一定不易者言之。则亦是信也。是其所指之地头。虽有此五个。而究其实则只是一个水也。人性之名有五。而实一理者。何以异于此哉。故孟子之论仁智。则曰不仁不智。朱子释之。则曰不仁故不智。于此可知仁与智之不为二物也。推之义与礼与信。莫不皆然。而近世一种学者。乃以无形之性。看作有形之物。而论禽兽之各通一路曰。虎狼只得仁。而义礼智信。则初不禀得。蜂蚁只得义。而仁礼智信。则都不禀得。雎鸠之别。鸿雁之序。候虫之信。莫不皆然云。则其乱道误说。得罪于圣贤之门。为如何哉。
指之名目。虽有五个地头。而究其实。则一个浑然之理也。譬以水。水只是一个活动之物。而以其润物生物之德而言之。则可谓之仁也。以其决裂壅塞之性而言之。则可谓之义也。以其泽水之有节。波浪之成纹而言之。则亦可谓节文之礼也。以其虚明之体。能受物之影象。而物之妍媸莫能遁。其形者而言之。则亦可谓之分辨之智也。以其润下之性一定不易者言之。则亦是信也。是其所指之地头。虽有此五个。而究其实则只是一个水也。人性之名有五。而实一理者。何以异于此哉。故孟子之论仁智。则曰不仁不智。朱子释之。则曰不仁故不智。于此可知仁与智之不为二物也。推之义与礼与信。莫不皆然。而近世一种学者。乃以无形之性。看作有形之物。而论禽兽之各通一路曰。虎狼只得仁。而义礼智信。则初不禀得。蜂蚁只得义。而仁礼智信。则都不禀得。雎鸠之别。鸿雁之序。候虫之信。莫不皆然云。则其乱道误说。得罪于圣贤之门。为如何哉。论井田说
井田之法废而制民之产不均。买卖之道出而兼并之弊生焉。富者。有十家之产。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以。一家安居。十家流亡。一人饶财。十人败家。人心由是而日诈。风俗由是而日薄。邦本安得而固乎。教化安得而行乎。此孟子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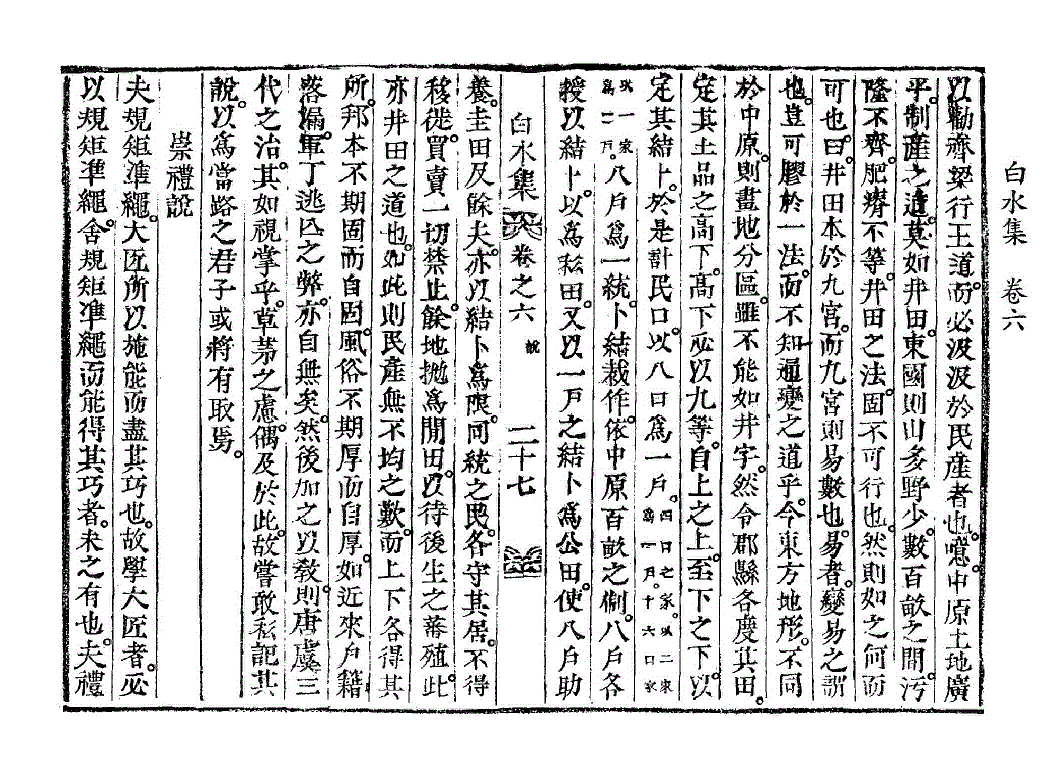 以劝齐梁行王道。而必汲汲于民产者也。噫。中原土地广平。制产之道。莫如井田。东国则山多野少。数百亩之间。污隆不齐。肥瘠不等。井田之法。固不可行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井田本于九宫。而九宫则易数也。易者。变易之谓也。岂可胶于一法。而不知通变之道乎。今东方地形。不同于中原。则画地分区。虽不能如井字。然令郡县各度其田。定其土品之高下。高下必以九等。自上之上。至下之下。以定其结卜。于是计民口。以八口为一户。(四口之家。以二家为一户。十六口家以一家为二户。)八户为一统。卜结裁作。依中原百亩之制。八户各授以结卜。以为私田。又以一户之结卜为公田。使八户助养。圭田及馀夫。亦以结卜为限。同统之民。各守其居。不得移徙。买卖一切禁止。馀地抛为閒田。以待后生之蕃殖。此亦井田之道也。如此则民产无不均之叹。而上下各得其所。邦本不期固而自固。风俗不期厚而自厚。如近来户籍落漏。军丁逃亡之弊。亦自无矣。然后加之以教。则唐虞三代之治。其如视掌乎。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尝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或将有取焉。
以劝齐梁行王道。而必汲汲于民产者也。噫。中原土地广平。制产之道。莫如井田。东国则山多野少。数百亩之间。污隆不齐。肥瘠不等。井田之法。固不可行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井田本于九宫。而九宫则易数也。易者。变易之谓也。岂可胶于一法。而不知通变之道乎。今东方地形。不同于中原。则画地分区。虽不能如井字。然令郡县各度其田。定其土品之高下。高下必以九等。自上之上。至下之下。以定其结卜。于是计民口。以八口为一户。(四口之家。以二家为一户。十六口家以一家为二户。)八户为一统。卜结裁作。依中原百亩之制。八户各授以结卜。以为私田。又以一户之结卜为公田。使八户助养。圭田及馀夫。亦以结卜为限。同统之民。各守其居。不得移徙。买卖一切禁止。馀地抛为閒田。以待后生之蕃殖。此亦井田之道也。如此则民产无不均之叹。而上下各得其所。邦本不期固而自固。风俗不期厚而自厚。如近来户籍落漏。军丁逃亡之弊。亦自无矣。然后加之以教。则唐虞三代之治。其如视掌乎。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尝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或将有取焉。崇礼说
夫规矩准绳。大匠所以施能而尽其巧也。故学大匠者。必以规矩准绳。舍规矩准绳而能得其巧者。未之有也。夫礼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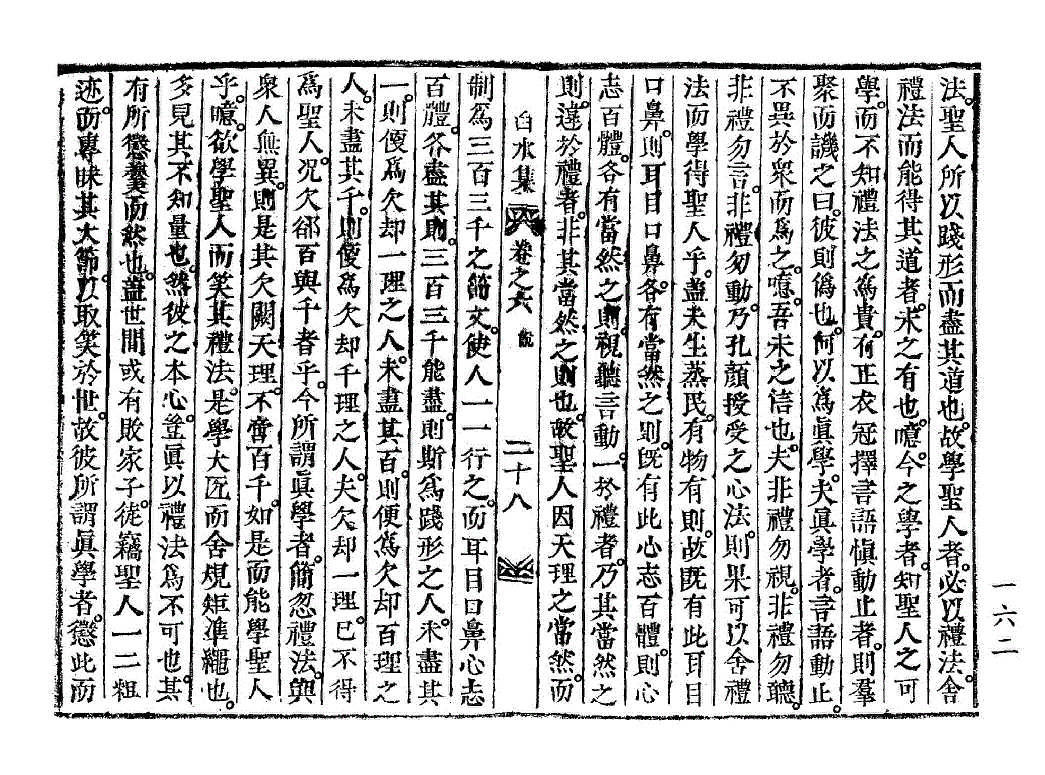 法。圣人所以践形而尽其道也。故学圣人者。必以礼法。舍礼法而能得其道者。未之有也。噫。今之学者。知圣人之可学。而不知礼法之为贵。有正衣冠择言语慎动止者。则群聚而讥之曰。彼则伪也。何以为真学。夫真学者。言语动止。不异于众而为之。噫。吾未之信也。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乃孔颜授受之心法。则果可以舍礼法而学得圣人乎。盖夫生蒸民。有物有则。故既有此耳目口鼻。则耳目口鼻。各有当然之则。既有此心志百体。则心志百体。各有当然之则。视听言动。一于礼者。乃其当然之则。违于礼者。非其当然之则也。故圣人因天理之当然。而制为三百三千之节文。使人一一行之。而耳目口鼻心志百体。各尽其则。三百三千能尽。则斯为践形之人。未尽其一。则便为欠却一理之人。未尽其百。则便为欠却百理之人。未尽其千。则便为欠却千理之人。夫欠却一理。已不得为圣人。况欠郤百与千者乎。今所谓真学者。简忽礼法。与众人无异。则是其欠阙天理。不啻百千。如是而能学圣人乎。噫。欲学圣人而笑其礼法。是学大匠而舍规矩准绳也。多见其不知量也。然彼之本心。岂真以礼法为不可也。其有所惩羹而然也。盖世间或有败家子。徒窃圣人一二粗迹。而专昧其大节。以取笑于世。故彼所谓真学者。惩此而
法。圣人所以践形而尽其道也。故学圣人者。必以礼法。舍礼法而能得其道者。未之有也。噫。今之学者。知圣人之可学。而不知礼法之为贵。有正衣冠择言语慎动止者。则群聚而讥之曰。彼则伪也。何以为真学。夫真学者。言语动止。不异于众而为之。噫。吾未之信也。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乃孔颜授受之心法。则果可以舍礼法而学得圣人乎。盖夫生蒸民。有物有则。故既有此耳目口鼻。则耳目口鼻。各有当然之则。既有此心志百体。则心志百体。各有当然之则。视听言动。一于礼者。乃其当然之则。违于礼者。非其当然之则也。故圣人因天理之当然。而制为三百三千之节文。使人一一行之。而耳目口鼻心志百体。各尽其则。三百三千能尽。则斯为践形之人。未尽其一。则便为欠却一理之人。未尽其百。则便为欠却百理之人。未尽其千。则便为欠却千理之人。夫欠却一理。已不得为圣人。况欠郤百与千者乎。今所谓真学者。简忽礼法。与众人无异。则是其欠阙天理。不啻百千。如是而能学圣人乎。噫。欲学圣人而笑其礼法。是学大匠而舍规矩准绳也。多见其不知量也。然彼之本心。岂真以礼法为不可也。其有所惩羹而然也。盖世间或有败家子。徒窃圣人一二粗迹。而专昧其大节。以取笑于世。故彼所谓真学者。惩此而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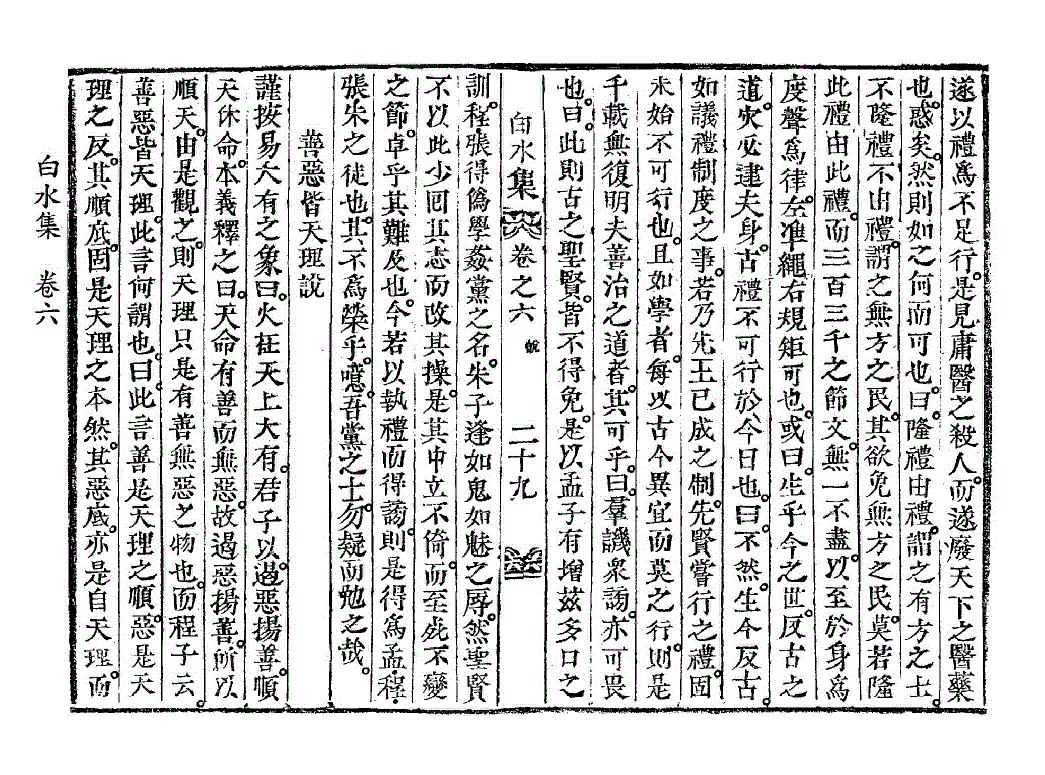 遂以礼为不足行。是见庸医之杀人。而遂废天下之医药也。惑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其欲免无方之民。莫若隆此礼由此礼。而三百三千之节文。无一不尽。以至于身为度声为律。左准绳右规矩可也。或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逮夫身。古礼不可行于今日也。曰。不然。生今反古。如议礼制度之事。若乃先王已成之制。先贤尝行之礼。固未始不可行也。且如学者。每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则是千载无复明夫善治之道者。其可乎。曰。群讥众谤。亦可畏也。曰。此则古之圣贤。皆不得免。是以孟子有增玆多口之训。程,张得伪学奸党之名。朱子逢如鬼如魅之辱。然圣贤不以此少回其志而改其操。是其中立不倚。而至死不变之节。卓乎其难及也。今若以执礼而得谤。则是得为孟,程,张,朱之徒也。其不为荣乎。噫。吾党之士。勿疑而勉之哉。
遂以礼为不足行。是见庸医之杀人。而遂废天下之医药也。惑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其欲免无方之民。莫若隆此礼由此礼。而三百三千之节文。无一不尽。以至于身为度声为律。左准绳右规矩可也。或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逮夫身。古礼不可行于今日也。曰。不然。生今反古。如议礼制度之事。若乃先王已成之制。先贤尝行之礼。固未始不可行也。且如学者。每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则是千载无复明夫善治之道者。其可乎。曰。群讥众谤。亦可畏也。曰。此则古之圣贤。皆不得免。是以孟子有增玆多口之训。程,张得伪学奸党之名。朱子逢如鬼如魅之辱。然圣贤不以此少回其志而改其操。是其中立不倚。而至死不变之节。卓乎其难及也。今若以执礼而得谤。则是得为孟,程,张,朱之徒也。其不为荣乎。噫。吾党之士。勿疑而勉之哉。善恶皆天理说
谨按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本义释之曰。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由是观之。则天理只是有善无恶之物也。而程子云。善恶皆天理。此言何谓也。曰。此言善是天理之顺。恶是天理之反。其顺底。固是天理之本然。其恶底。亦是自天理。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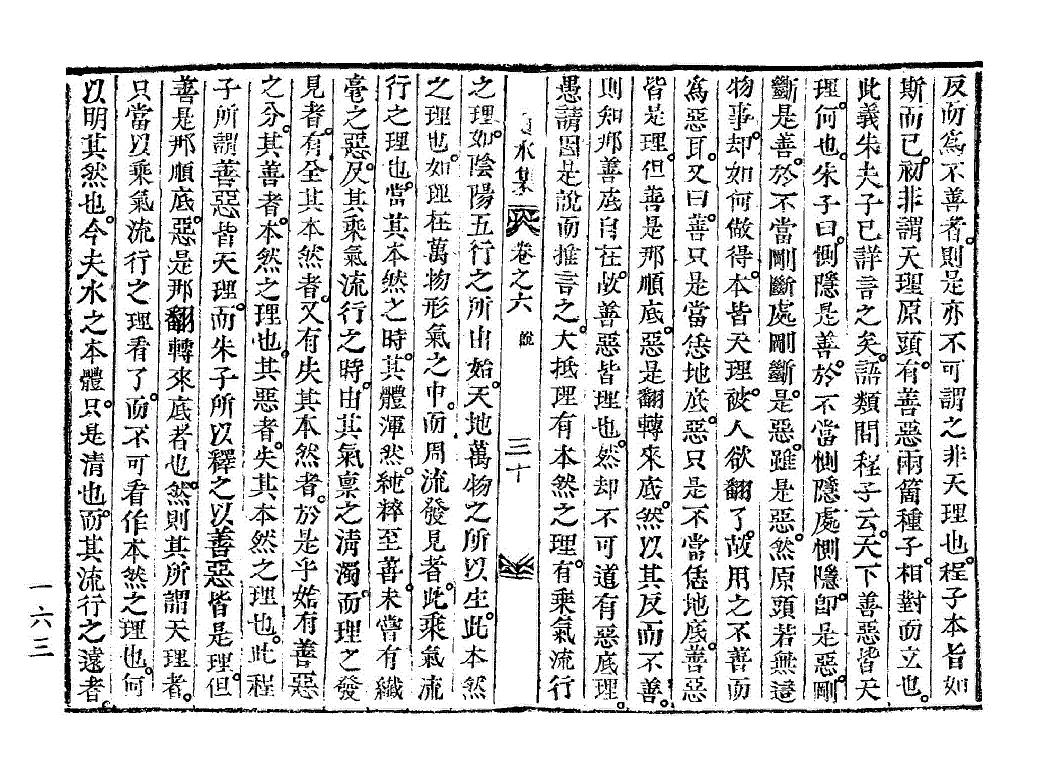 反而为不善者。则是亦不可谓之非天理也。程子本旨如斯而已。初非谓天理原头。有善恶两个种子。相对而立也。此义朱夫子已详言之矣。语类问程子云。天下善恶皆天理。何也。朱子曰。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刚断是善。于不当刚断处刚断。是恶。虽是恶。然原头若无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又曰。善只是当恁地底。恶只是不当恁地底。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翻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愚请因是说而推言之。大抵理有本然之理。有乘气流行之理。如阴阳五行之所由始。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此本然之理也。如理在万物形气之中。而周流发见者。此乘气流行之理也。当其本然之时。其体浑然。纯粹至善。未尝有纤毫之恶。及其乘气流行之时。由其气禀之清浊。而理之发见者。有全其本然者。又有失其本然者。于是乎始有善恶之分。其善者。本然之理也。其恶者。失其本然之理也。此程子所谓善恶皆天理。而朱子所以释之以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那翻转来底者也。然则其所谓天理者。只当以乘气流行之理看了。而不可看作本然之理也。何以明其然也。今夫水之本体。只是清也。而其流行之远者。
反而为不善者。则是亦不可谓之非天理也。程子本旨如斯而已。初非谓天理原头。有善恶两个种子。相对而立也。此义朱夫子已详言之矣。语类问程子云。天下善恶皆天理。何也。朱子曰。恻隐是善。于不当恻隐处恻隐。即是恶。刚断是善。于不当刚断处刚断。是恶。虽是恶。然原头若无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为恶耳。又曰。善只是当恁地底。恶只是不当恁地底。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翻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愚请因是说而推言之。大抵理有本然之理。有乘气流行之理。如阴阳五行之所由始。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此本然之理也。如理在万物形气之中。而周流发见者。此乘气流行之理也。当其本然之时。其体浑然。纯粹至善。未尝有纤毫之恶。及其乘气流行之时。由其气禀之清浊。而理之发见者。有全其本然者。又有失其本然者。于是乎始有善恶之分。其善者。本然之理也。其恶者。失其本然之理也。此程子所谓善恶皆天理。而朱子所以释之以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那翻转来底者也。然则其所谓天理者。只当以乘气流行之理看了。而不可看作本然之理也。何以明其然也。今夫水之本体。只是清也。而其流行之远者。白水先生文集卷之六 第 1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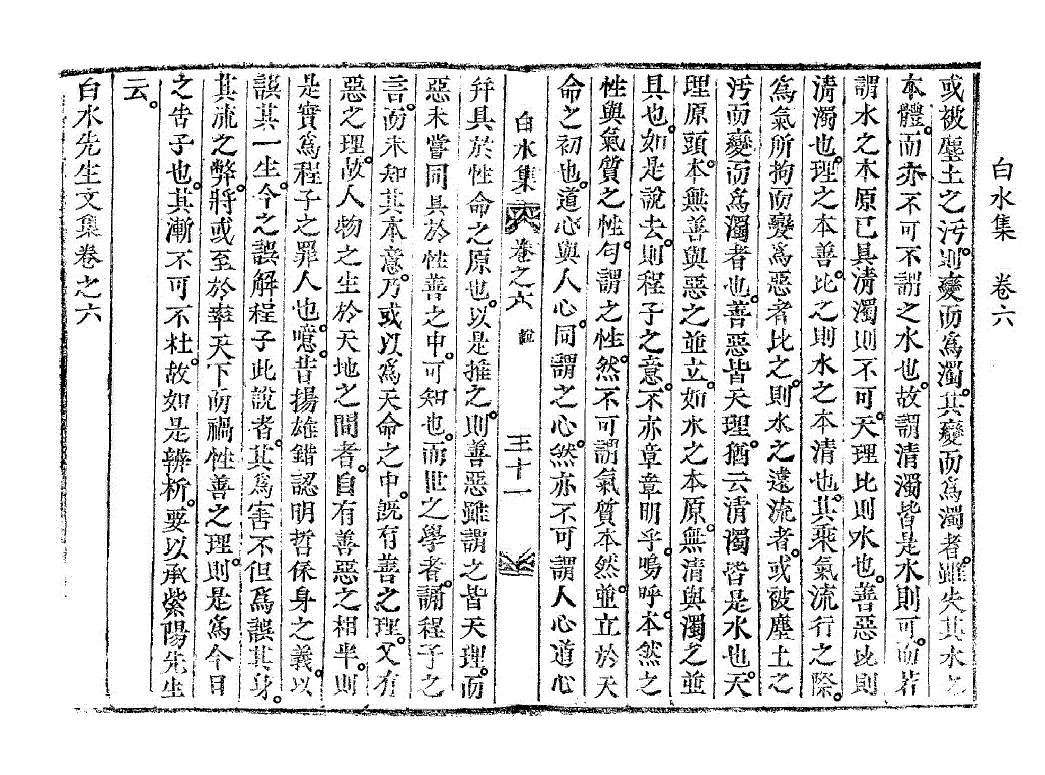 或被尘土之污。则变而为浊。其变而为浊者。虽失其水之本体。而亦不可不谓之水也。故谓清浊皆是水则可。而若谓水之本原已具清浊则不可。天理比则水也。善恶比则清浊也。理之本善。比之则水之本清也。其乘气流行之际。为气所拘而变为恶者比之。则水之远流者。或被尘土之污而变而为浊者也。善恶皆天理。犹云清浊皆是水也。天理原头。本无善与恶之并立。如水之本原。无清与浊之并具也。如是说去。则程子之意。不亦章章明乎。呜呼。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匀谓之性。然不可谓气质本然。并立于天命之初也。道心与人心。同谓之心。然亦不可谓人心道心并具于性命之原也。以是推之。则善恶虽谓之皆天理。而恶未尝同具于性善之中。可知也。而世之学者。诵程子之言。而未知其本意。乃或以为天命之中。既有善之理。又有恶之理。故人物之生于天地之间者。自有善恶之相半。则是实为程子之罪人也。噫。昔扬雄错认明哲保身之义。以误其一生。今之误解程子此说者。其为害不但为误其身。其流之弊。将或至于率天下而祸性善之理。则是为今日之告子也。其渐不可不杜。故如是辨析。要以承紫阳先生云。
或被尘土之污。则变而为浊。其变而为浊者。虽失其水之本体。而亦不可不谓之水也。故谓清浊皆是水则可。而若谓水之本原已具清浊则不可。天理比则水也。善恶比则清浊也。理之本善。比之则水之本清也。其乘气流行之际。为气所拘而变为恶者比之。则水之远流者。或被尘土之污而变而为浊者也。善恶皆天理。犹云清浊皆是水也。天理原头。本无善与恶之并立。如水之本原。无清与浊之并具也。如是说去。则程子之意。不亦章章明乎。呜呼。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匀谓之性。然不可谓气质本然。并立于天命之初也。道心与人心。同谓之心。然亦不可谓人心道心并具于性命之原也。以是推之。则善恶虽谓之皆天理。而恶未尝同具于性善之中。可知也。而世之学者。诵程子之言。而未知其本意。乃或以为天命之中。既有善之理。又有恶之理。故人物之生于天地之间者。自有善恶之相半。则是实为程子之罪人也。噫。昔扬雄错认明哲保身之义。以误其一生。今之误解程子此说者。其为害不但为误其身。其流之弊。将或至于率天下而祸性善之理。则是为今日之告子也。其渐不可不杜。故如是辨析。要以承紫阳先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