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书
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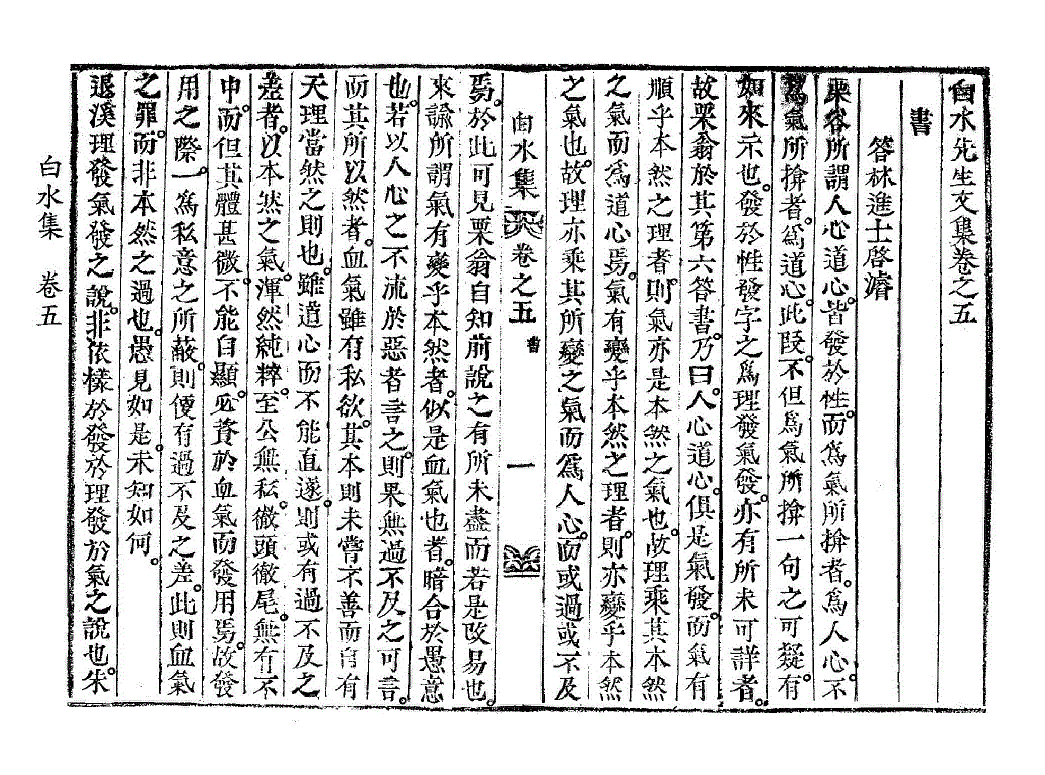 答林进士(启浚)
答林进士(启浚)栗谷所谓人心道心。皆发于性。而为气所掩者。为人心。不为气所掩者。为道心。此段。不但为气所掩一句之可疑。有如来示也。发于性发字之为理发气发。亦有所未可详者。故栗翁于其第六答书。乃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于此可见栗翁自知前说之有所未尽而若是改易也。来谕所谓气有变乎本然者。似是血气也者。暗合于愚意也。若以人心之不流于恶者言之。则果无过不及之可言。而其所以然者。血气虽有私欲。其本则未尝不善而自有天理当然之则也。虽道心而不能直遂。则或有过不及之差者。以本然之气。浑然纯粹。至公无私。彻头彻尾。无有不中。而但其体甚微。不能自显。必资于血气而发用焉。故发用之际。一为私意之所蔽。则便有过不及之差。此则血气之罪。而非本然之过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退溪理发气发之说。非依样于发于理发于气之说也。朱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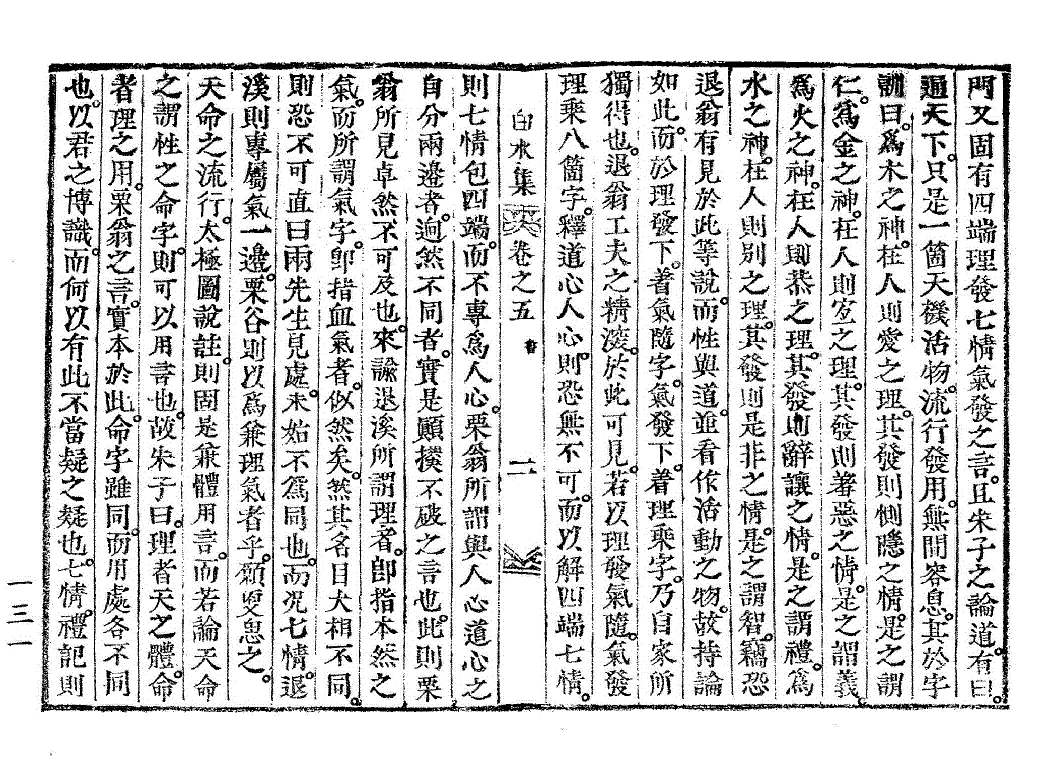 门又固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且朱子之论道。有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其于字训曰。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让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窃恐退翁有见于此等说。而性与道。并看作活动之物。故持论如此。而于理发下。着气随字。气发下。着理乘字。乃自家所独得也。退翁工夫之精深。于此可见。若以理发气随。气发理乘八个字。释道心人心。则恐无不可。而以解四端七情。则七情包四端。而不专为人心。栗翁所谓与人心道心之自分两边者。迥然不同者。实是颠扑不破之言也。此则栗翁所见卓然不可及也。来谕退溪所谓理者。即指本然之气。而所谓气字。即指血气者。似然矣。然其名目大相不同。则恐不可直曰两先生见处。未始不为同也。而况七情。退溪则专属气一边。栗谷则以为兼理气者乎。愿更思之。
门又固有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之言。且朱子之论道。有曰。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其于字训曰。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为金之神。在人则宜之理。其发则羞恶之情。是之谓义。为火之神。在人则恭之理。其发则辞让之情。是之谓礼。为水之神。在人则别之理。其发则是非之情。是之谓智。窃恐退翁有见于此等说。而性与道。并看作活动之物。故持论如此。而于理发下。着气随字。气发下。着理乘字。乃自家所独得也。退翁工夫之精深。于此可见。若以理发气随。气发理乘八个字。释道心人心。则恐无不可。而以解四端七情。则七情包四端。而不专为人心。栗翁所谓与人心道心之自分两边者。迥然不同者。实是颠扑不破之言也。此则栗翁所见卓然不可及也。来谕退溪所谓理者。即指本然之气。而所谓气字。即指血气者。似然矣。然其名目大相不同。则恐不可直曰两先生见处。未始不为同也。而况七情。退溪则专属气一边。栗谷则以为兼理气者乎。愿更思之。天命之流行。太极图说注。则固是兼体用言。而若论天命之谓性之命字。则可以用言也。故朱子曰。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栗翁之言。实本于此。命字虽同。而用处各不同也。以君之博识。而何以有此不当疑之疑也。七情。礼记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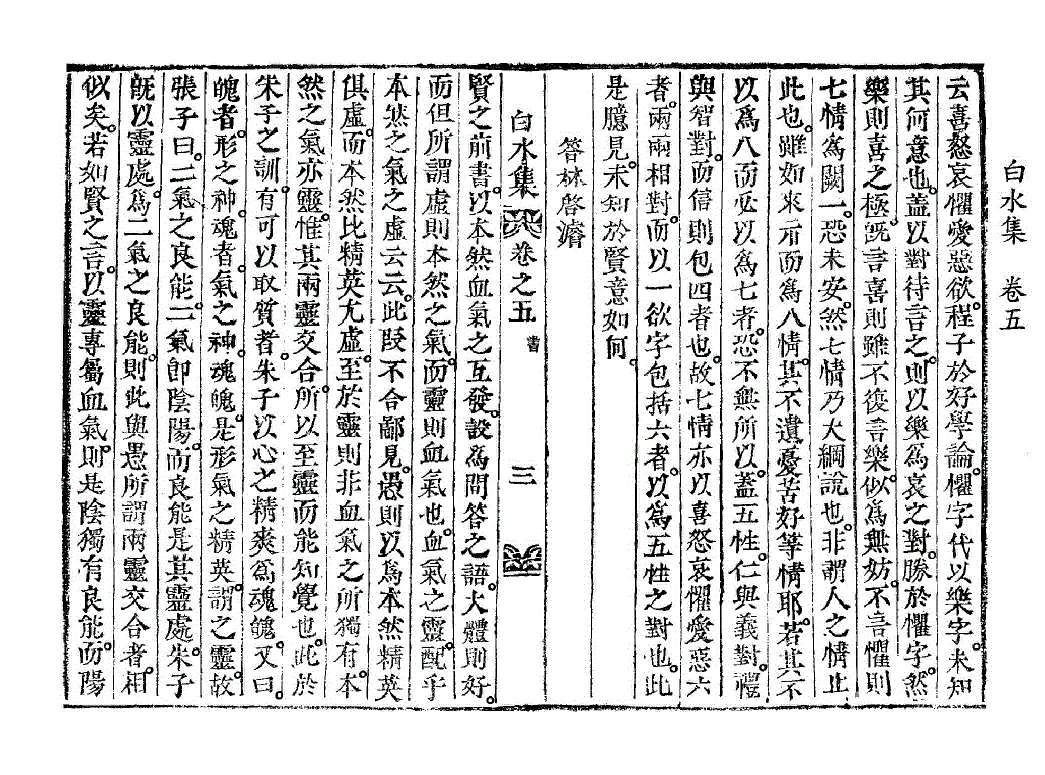 云喜怒哀惧爱恶欲。程子于好学论。惧字代以乐字。未知其何意也。盖以对待言之。则以乐为哀之对。胜于惧字。然乐则喜之极。既言喜则虽不复言乐。似为无妨。不言惧则七情为阙一。恐未安。然七情乃大纲说也。非谓人之情止此也。虽如来示而为八情。其不遗忧苦好等情耶。若其不以为八而必以为七者。恐不无所以。盖五性。仁与义对。礼与智对。而信则包四者也。故七情亦以喜怒哀惧爱恶六者。两两相对。而以一欲字包括六者。以为五性之对也。此是臆见。未知于贤意如何。
云喜怒哀惧爱恶欲。程子于好学论。惧字代以乐字。未知其何意也。盖以对待言之。则以乐为哀之对。胜于惧字。然乐则喜之极。既言喜则虽不复言乐。似为无妨。不言惧则七情为阙一。恐未安。然七情乃大纲说也。非谓人之情止此也。虽如来示而为八情。其不遗忧苦好等情耶。若其不以为八而必以为七者。恐不无所以。盖五性。仁与义对。礼与智对。而信则包四者也。故七情亦以喜怒哀惧爱恶六者。两两相对。而以一欲字包括六者。以为五性之对也。此是臆见。未知于贤意如何。答林启浚
贤之前书。以本然血气之互发。设为问答之语。大体则好。而但所谓虚则本然之气。而灵则血气也。血气之灵。配乎本然之气之虚云云。此段不合鄙见。愚则以为本然精英俱虚。而本然比精英尤虚。至于灵则非血气之所独有。本然之气亦灵。惟其两灵交合。所以至灵而能知觉也。此于朱子之训。有可以取质者。朱子以心之精爽为魂魄。又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魂魄。是形气之精英。谓之灵。故张子曰。二气之良能。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朱子既以灵处。为二气之良能。则此与愚所谓两灵交合者。相似矣。若如贤之言。以灵专属血气。则是阴独有良能。而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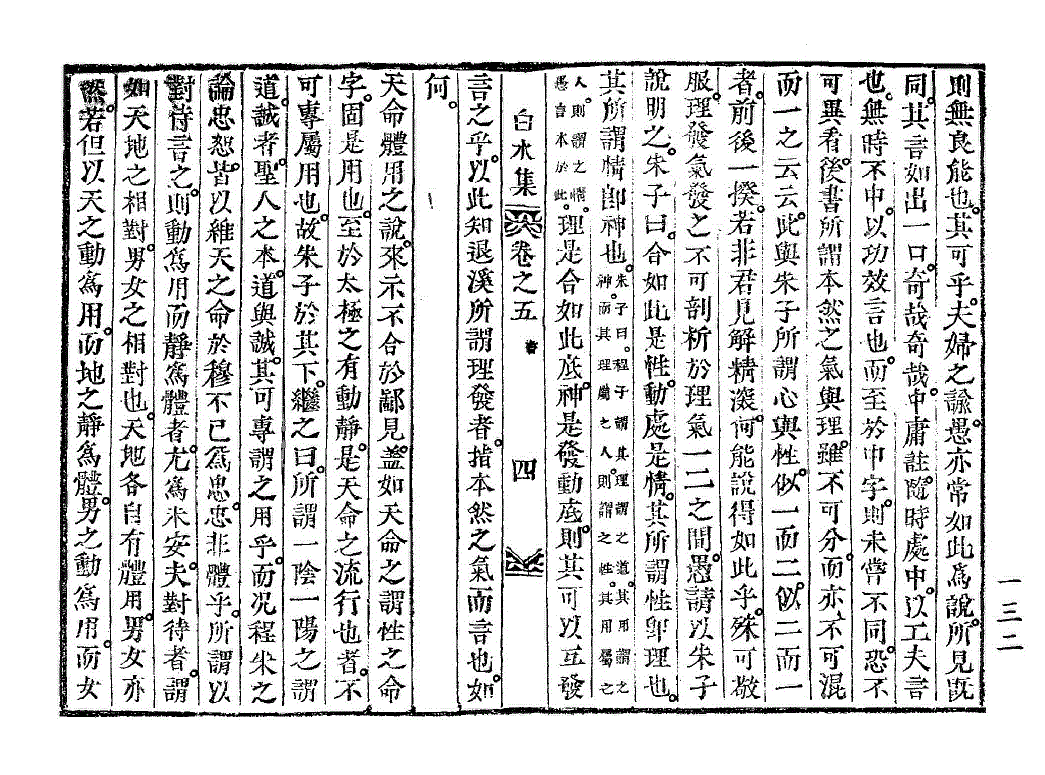 则无良能也。其可乎。夫妇之谕。愚亦常如此为说。所见既同。其言如出一口。奇哉奇哉。中庸注。随时处中。以工夫言也。无时不中。以功效言也。而至于中字。则未尝不同。恐不可异看。后书所谓本然之气与理。虽不可分。而亦不可混而一之云云。此与朱子所谓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者。前后一揆。若非君见解精深。何能说得如此乎。殊可敬服。理发气发之不可剖析于理气一二之间。愚请以朱子说明之。朱子曰。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其所谓性即理也。其所谓情即神也。(朱子曰。程子谓其理谓之道。其用谓之神。而其理属之人。则谓之性。其用属之人。则谓之情。愚言本于此。)理是合如此底。神是发动底。则其可以互发言之乎。以此知退溪所谓理发者。指本然之气而言也。如何。
则无良能也。其可乎。夫妇之谕。愚亦常如此为说。所见既同。其言如出一口。奇哉奇哉。中庸注。随时处中。以工夫言也。无时不中。以功效言也。而至于中字。则未尝不同。恐不可异看。后书所谓本然之气与理。虽不可分。而亦不可混而一之云云。此与朱子所谓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者。前后一揆。若非君见解精深。何能说得如此乎。殊可敬服。理发气发之不可剖析于理气一二之间。愚请以朱子说明之。朱子曰。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其所谓性即理也。其所谓情即神也。(朱子曰。程子谓其理谓之道。其用谓之神。而其理属之人。则谓之性。其用属之人。则谓之情。愚言本于此。)理是合如此底。神是发动底。则其可以互发言之乎。以此知退溪所谓理发者。指本然之气而言也。如何。天命体用之说。来示不合于鄙见。盖如天命之谓性之命字。固是用也。至于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者。不可专属用也。故朱子于其下。继之曰。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道与诚。其可专谓之用乎。而况程朱之论忠恕。皆以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为忠。忠非体乎。所谓以对待言之。则动为用而静为体者。尤为未安。夫对待者。谓如天地之相对。男女之相对也。天地各自有体用。男女亦然。若但以天之动为用。而地之静为体。男之动为用。而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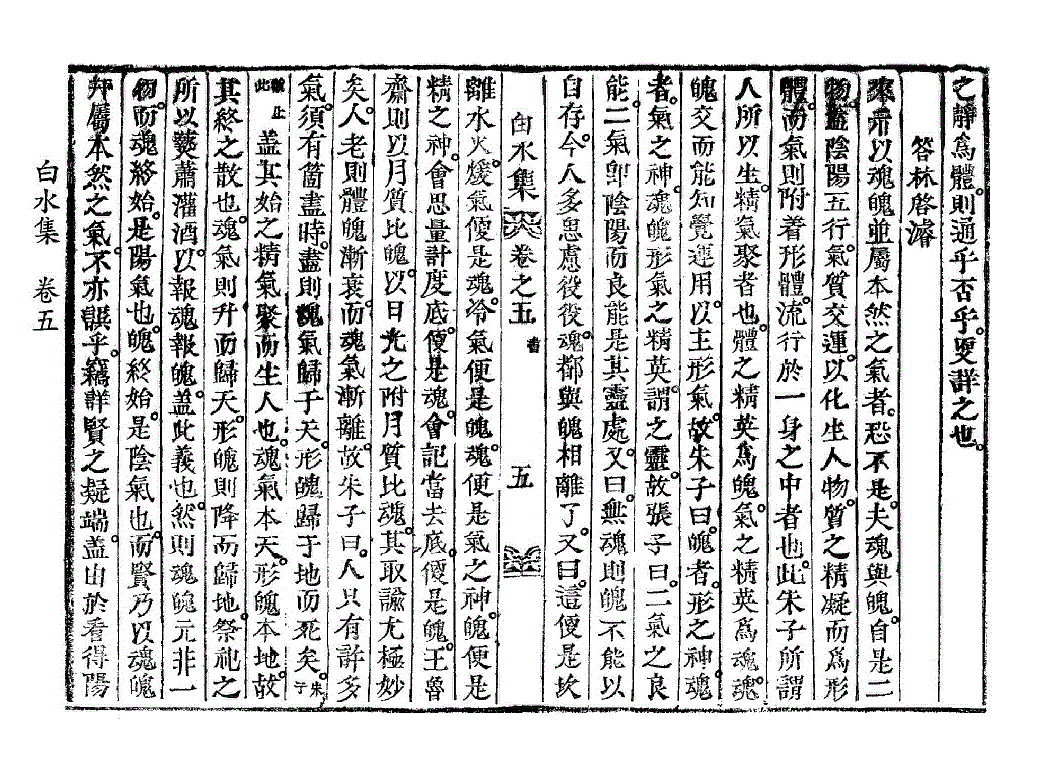 之静为体。则通乎否乎。更详之也。
之静为体。则通乎否乎。更详之也。答林启浚
来示以魂魄并属本然之气者。恐不是。夫魂与魄。自是二物。盖阴阳五行。气质交运。以化生人物。质之精凝而为形体。而气则附着形体。流行于一身之中者也。此朱子所谓人所以生。精气聚者也。体之精英为魄。气之精英为魂。魂魄交而能知觉运用。以主形气。故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气之神。魂魄形气之精英。谓之灵。故张子曰。二气之良能。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又曰。无魂则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虑役役。魂都与魄相离了。又曰。这便是坎离水火。煖气便是魂。冷气便是魄。魂便是气之神。魄便是精之神。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王鲁斋则以月质比魄。以日光之附月质比魂。其取谕尤极妙矣。人老则体魄渐衰。而魂气渐离。故朱子曰。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朱子说止此)盖其始之精气聚而生人也。魂气本天。形魄本地。故其终之散也。魂气则升而归天。形魄则降而归地。祭祀之所以爇萧灌酒。以报魂报魄。盖此义也。然则魂魄元非一物。而魂终始。是阳气也。魄终始。是阴气也。而贤乃以魂魄并属本然之气。不亦误乎。窃详贤之疑端。盖由于看得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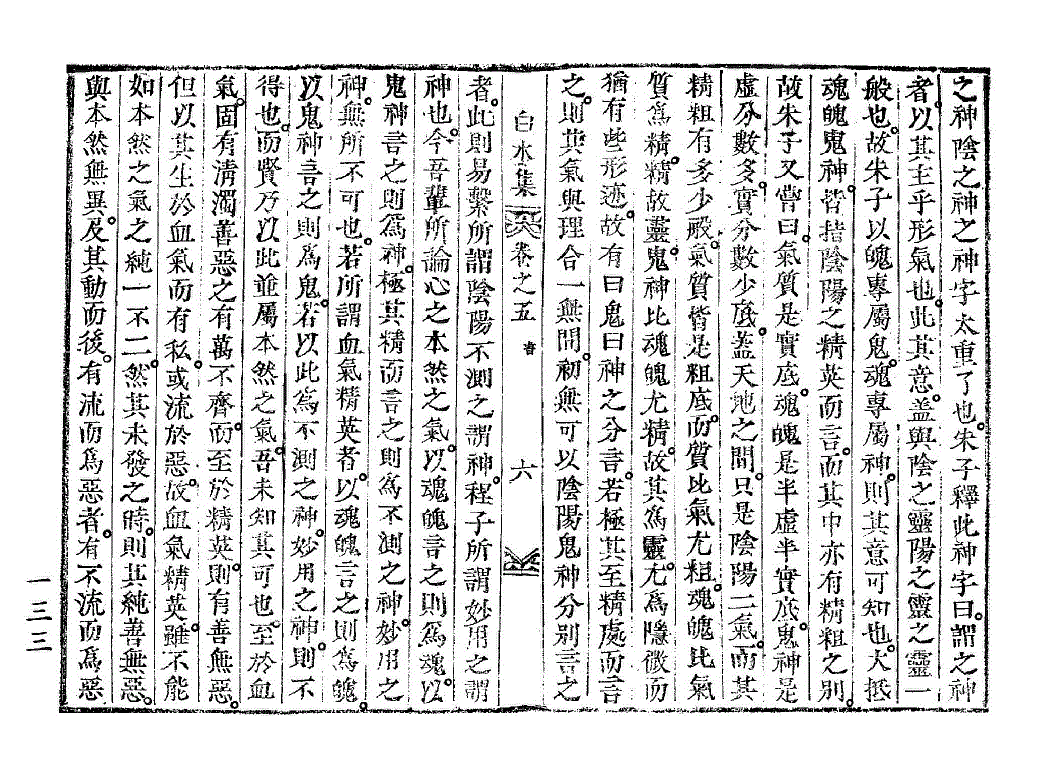 之神阴之神之神字太重了也。朱子释此神字曰。谓之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此其意。盖与阴之灵阳之灵之灵一般也。故朱子以魄专属鬼。魂专属神。则其意可知也。大抵魂魄鬼神。皆指阴阳之精英而言。而其中亦有精粗之别。故朱子又尝曰。气质是实底。魂魄是半虚半实底。鬼神是虚分数多。实分数少底。盖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二气。而其精粗有多少般。气质皆是粗底。而质比气尤粗。魂魄比气质为精。精故灵。鬼神比魂魄尤精。故其为灵。尤为隐微而犹有些形迹。故有曰鬼曰神之分言。若极其至精处而言之。则其气与理合一无间。初无可以阴阳鬼神分别言之者。此则易系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程子所谓妙用之谓神也。今吾辈所论心之本然之气。以魂魄言之则为魂。以鬼神言之则为神。极其精而言之则为不测之神。妙用之神。无所不可也。若所谓血气精英者。以魂魄言之则为魄。以鬼神言之则为鬼。若以此为不测之神。妙用之神。则不得也。而贤乃以此并属本然之气。吾未知其可也。至于血气。固有清浊善恶之有万不齐。而至于精英。则有善无恶。但以其生于血气而有私。或流于恶。故血气精英。虽不能如本然之气之纯一不二。然其未发之时。则其纯善无恶。与本然无异。及其动而后。有流而为恶者。有不流而为恶
之神阴之神之神字太重了也。朱子释此神字曰。谓之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此其意。盖与阴之灵阳之灵之灵一般也。故朱子以魄专属鬼。魂专属神。则其意可知也。大抵魂魄鬼神。皆指阴阳之精英而言。而其中亦有精粗之别。故朱子又尝曰。气质是实底。魂魄是半虚半实底。鬼神是虚分数多。实分数少底。盖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二气。而其精粗有多少般。气质皆是粗底。而质比气尤粗。魂魄比气质为精。精故灵。鬼神比魂魄尤精。故其为灵。尤为隐微而犹有些形迹。故有曰鬼曰神之分言。若极其至精处而言之。则其气与理合一无间。初无可以阴阳鬼神分别言之者。此则易系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程子所谓妙用之谓神也。今吾辈所论心之本然之气。以魂魄言之则为魂。以鬼神言之则为神。极其精而言之则为不测之神。妙用之神。无所不可也。若所谓血气精英者。以魂魄言之则为魄。以鬼神言之则为鬼。若以此为不测之神。妙用之神。则不得也。而贤乃以此并属本然之气。吾未知其可也。至于血气。固有清浊善恶之有万不齐。而至于精英。则有善无恶。但以其生于血气而有私。或流于恶。故血气精英。虽不能如本然之气之纯一不二。然其未发之时。则其纯善无恶。与本然无异。及其动而后。有流而为恶者。有不流而为恶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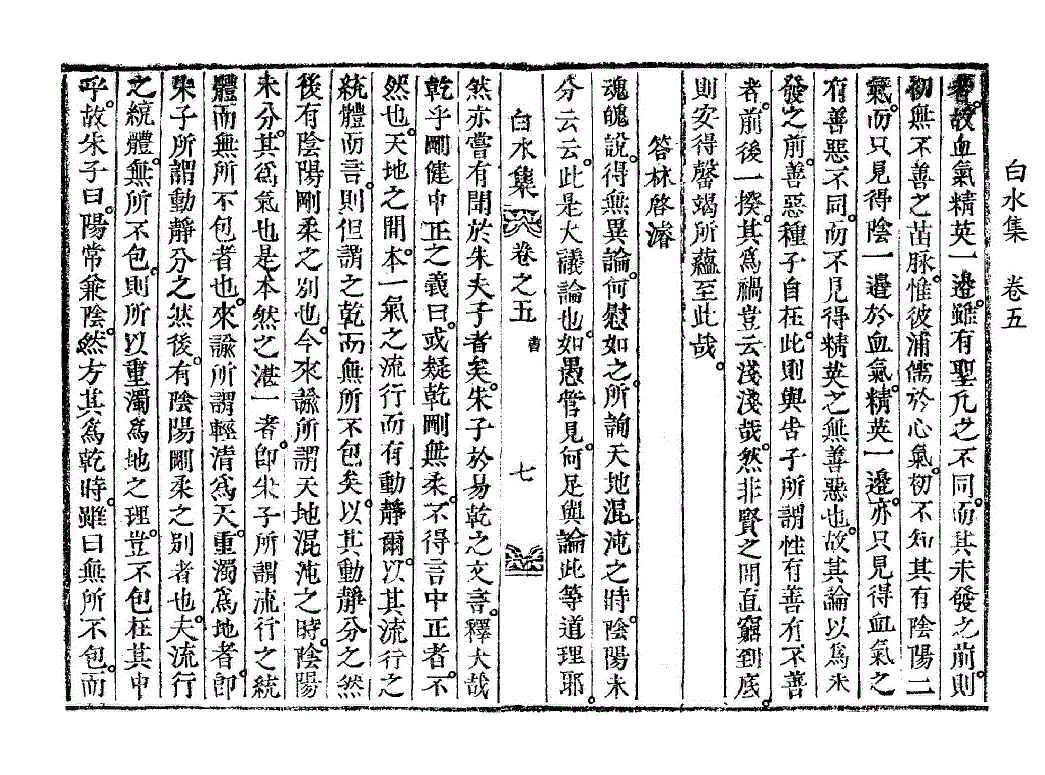 者。故血气精英一边。虽有圣凡之不同。而其未发之前。则初无不善之苗脉。惟彼浦儒于心气。初不知其有阴阳二气。而只见得阴一边于血气。精英一边。亦只见得血气之有善恶不同。而不见得精英之无善恶也。故其论以为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此则与告子所谓性有善有不善者。前后一揆。其为祸岂云浅浅哉。然非贤之问直穷到底。则安得罄竭所蕴至此哉。
者。故血气精英一边。虽有圣凡之不同。而其未发之前。则初无不善之苗脉。惟彼浦儒于心气。初不知其有阴阳二气。而只见得阴一边于血气。精英一边。亦只见得血气之有善恶不同。而不见得精英之无善恶也。故其论以为未发之前。善恶种子自在。此则与告子所谓性有善有不善者。前后一揆。其为祸岂云浅浅哉。然非贤之问直穷到底。则安得罄竭所蕴至此哉。答林启浚
魂魄说。得无异论。何慰如之。所询天地混沌之时。阴阳未分云云。此是大议论也。如愚管见。何足与论此等道理耶。然亦尝有闻于朱夫子者矣。朱子于易乾之文言。释大哉乾乎刚健中正之义曰。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今来谕所谓天地混沌之时。阴阳未分。其为气也是本然之湛一者。即朱子所谓流行之统体而无所不包者也。来谕所谓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者。即朱子所谓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者也。夫流行之统体。无所不包。则所以重浊为地之理。岂不包在其中乎。故朱子曰。阳常兼阴。然方其为乾时。虽曰无所不包。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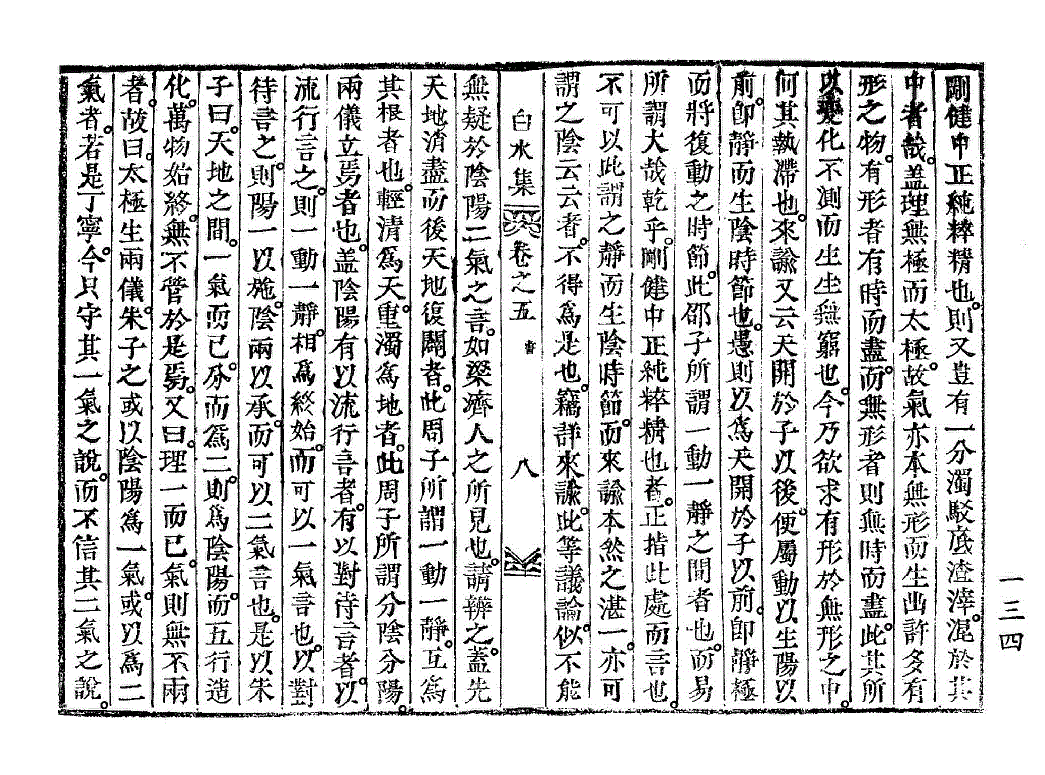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则又岂有一分浊驳底渣滓。混于其中者哉。盖理无极而太极。故气亦本无形而生出许多有形之物。有形者有时而尽。而无形者则无时而尽。此其所以变化不测而生生无穷也。今乃欲求有形于无形之中。何其执滞也。来谕又云天开于子以后。便属动以生阳以前。即静而生阴时节也。愚则以为天开于子以前。即静极而将复动之时节。此邵子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也。而易所谓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正指此处而言也。不可以此谓之静而生阴时节。而来谕本然之湛一。亦可谓之阴云云者。不得为是也。窃详来谕。此等议论。似不能无疑于阴阳二气之言。如梁济人之所见也。请辨之。盖先天地消尽而后天地复辟者。此周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也。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者。此周子所谓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盖阴阳有以流行言者。有以对待言者。以流行言之。则一动一静。相为终始。而可以一气言也。以对待言之。则阳一以施。阴两以承。而可以二气言也。是以朱子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又曰。理一而已。气则无不两者。故曰。太极生两仪。朱子之或以阴阳为一气。或以为二气者。若是丁宁。今只守其一气之说。而不信其二气之说。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则又岂有一分浊驳底渣滓。混于其中者哉。盖理无极而太极。故气亦本无形而生出许多有形之物。有形者有时而尽。而无形者则无时而尽。此其所以变化不测而生生无穷也。今乃欲求有形于无形之中。何其执滞也。来谕又云天开于子以后。便属动以生阳以前。即静而生阴时节也。愚则以为天开于子以前。即静极而将复动之时节。此邵子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也。而易所谓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正指此处而言也。不可以此谓之静而生阴时节。而来谕本然之湛一。亦可谓之阴云云者。不得为是也。窃详来谕。此等议论。似不能无疑于阴阳二气之言。如梁济人之所见也。请辨之。盖先天地消尽而后天地复辟者。此周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者也。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者。此周子所谓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盖阴阳有以流行言者。有以对待言者。以流行言之。则一动一静。相为终始。而可以一气言也。以对待言之。则阳一以施。阴两以承。而可以二气言也。是以朱子曰。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又曰。理一而已。气则无不两者。故曰。太极生两仪。朱子之或以阴阳为一气。或以为二气者。若是丁宁。今只守其一气之说。而不信其二气之说。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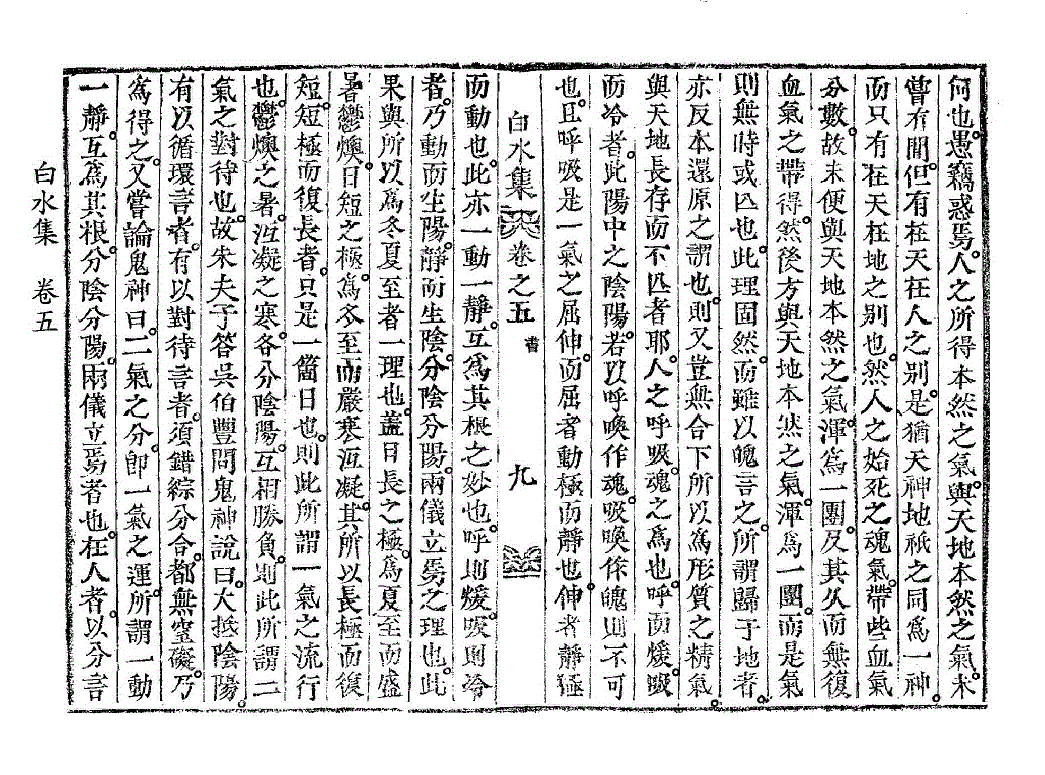 何也。愚窃惑焉。人之所得本然之气。与天地本然之气。未尝有间。但有在天在人之别。是犹天神地祇之同为一神。而只有在天在地之别也。然人之始死之魂气。带些血气分数。故未便与天地本然之气。浑为一团。及其久而无复血气之带得。然后方与天地本然之气。浑为一团。而是气则无时或亡也。此理固然。而虽以魄言之。所谓归于地者。亦反本还原之谓也。则又岂无合下所以为形质之精气。与天地长存而不亡者耶。人之呼吸。魂之为也。呼而煖。吸而冷者。此阳中之阴阳。若以呼唤作魂。吸唤作魄则不可也。且呼吸是一气之屈伸。而屈者动极而静也。伸者静极而动也。此亦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妙也。呼则煖。吸则冷者。乃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理也。此果与所以为冬夏至者一理也。盖日长之极。为夏至而盛暑郁燠。日短之极。为冬至而严寒冱凝。其所以长极而复短。短极而复长者。只是一个日也。则此所谓一气之流行也。郁燠之暑。冱凝之寒。各分阴阳。互相胜负。则此所谓二气之对待也。故朱夫子答吴伯丰问鬼神说曰。大抵阴阳。有以循环言者。有以对待言者。须错综分合。都无窒碍。乃为得之。又尝论鬼神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
何也。愚窃惑焉。人之所得本然之气。与天地本然之气。未尝有间。但有在天在人之别。是犹天神地祇之同为一神。而只有在天在地之别也。然人之始死之魂气。带些血气分数。故未便与天地本然之气。浑为一团。及其久而无复血气之带得。然后方与天地本然之气。浑为一团。而是气则无时或亡也。此理固然。而虽以魄言之。所谓归于地者。亦反本还原之谓也。则又岂无合下所以为形质之精气。与天地长存而不亡者耶。人之呼吸。魂之为也。呼而煖。吸而冷者。此阳中之阴阳。若以呼唤作魂。吸唤作魄则不可也。且呼吸是一气之屈伸。而屈者动极而静也。伸者静极而动也。此亦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妙也。呼则煖。吸则冷者。乃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理也。此果与所以为冬夏至者一理也。盖日长之极。为夏至而盛暑郁燠。日短之极。为冬至而严寒冱凝。其所以长极而复短。短极而复长者。只是一个日也。则此所谓一气之流行也。郁燠之暑。冱凝之寒。各分阴阳。互相胜负。则此所谓二气之对待也。故朱夫子答吴伯丰问鬼神说曰。大抵阴阳。有以循环言者。有以对待言者。须错综分合。都无窒碍。乃为得之。又尝论鬼神曰。二气之分。即一气之运。所谓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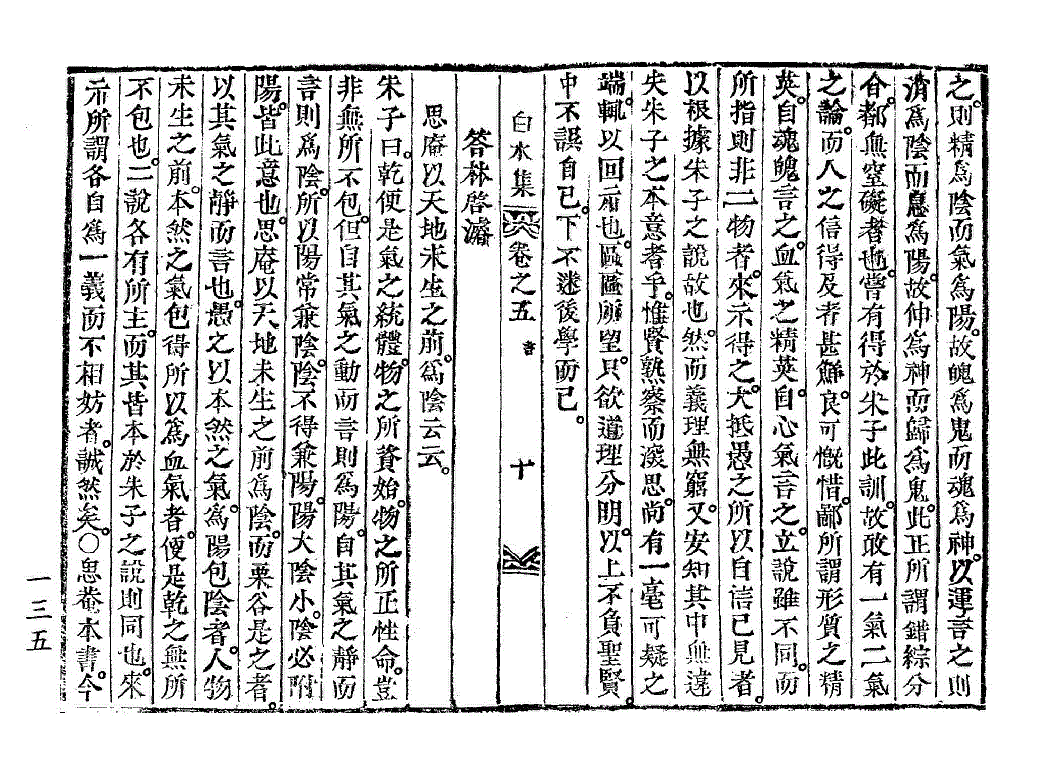 之。则精为阴而气为阳。故魄为鬼而魂为神。以运言之则消为阴而息为阳。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正所谓错综分合。都无窒碍者也。尝有得于朱子此训。故敢有一气二气之论。而人之信得及者甚鲜。良可慨惜。鄙所谓形质之精英。自魂魄言之。血气之精英。自心气言之。立说虽不同。而所指则非二物者。来示得之。大抵愚之所以自信己见者。以根据朱子之说故也。然而义理无穷。又安知其中无违失朱子之本意者乎。惟贤熟察而深思。尚有一毫可疑之端。辄以回示也。区区所望。只欲道理分明。以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
之。则精为阴而气为阳。故魄为鬼而魂为神。以运言之则消为阴而息为阳。故伸为神而归为鬼。此正所谓错综分合。都无窒碍者也。尝有得于朱子此训。故敢有一气二气之论。而人之信得及者甚鲜。良可慨惜。鄙所谓形质之精英。自魂魄言之。血气之精英。自心气言之。立说虽不同。而所指则非二物者。来示得之。大抵愚之所以自信己见者。以根据朱子之说故也。然而义理无穷。又安知其中无违失朱子之本意者乎。惟贤熟察而深思。尚有一毫可疑之端。辄以回示也。区区所望。只欲道理分明。以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答林启浚
思庵以天地未生之前。为阴云云。
朱子曰。乾便是气之统体。物之所资始。物之所正性命。岂非无所不包。但自其气之动而言则为阳。自其气之静而言则为阴。所以阳常兼阴。阴不得兼阳。阳大阴小。阴必附阳。皆此意也。思庵以天地未生之前为阴。而栗谷是之者。以其气之静而言也。愚之以本然之气。为阳包阴者。人物未生之前。本然之气包得所以为血气者。便是乾之无所不包也。二说各有所主。而其皆本于朱子之说则同也。来示所谓各自为一义而不相妨者。诚然矣。○思庵本书。今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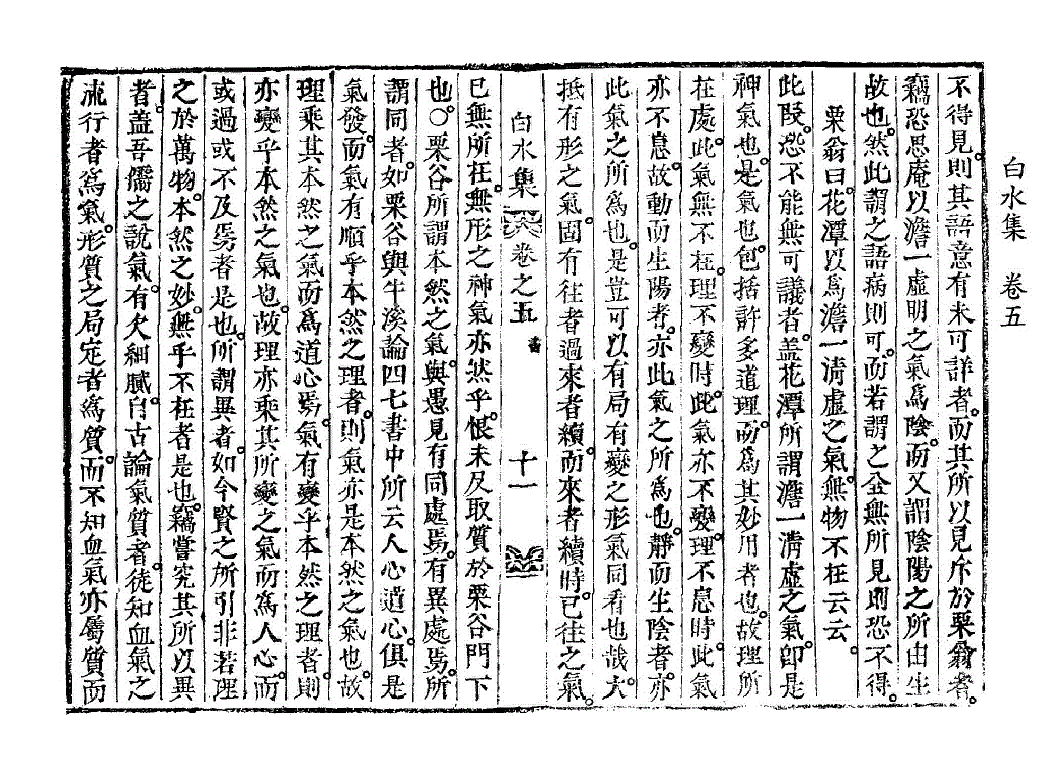 不得见。则其语意有未可详者。而其所以见斥于栗翁者。窃恐思庵以澹一虚明之气为阴。而又谓阴阳之所由生故也。然此谓之语病则可。而若谓之全无所见则恐不得。
不得见。则其语意有未可详者。而其所以见斥于栗翁者。窃恐思庵以澹一虚明之气为阴。而又谓阴阳之所由生故也。然此谓之语病则可。而若谓之全无所见则恐不得。栗翁曰。花潭以为澹一清虚之气。无物不在云云。
此段。恐不能无可议者。盖花潭所谓澹一清虚之气。即是神气也。是气也。包括许多道理。而为其妙用者也。故理所在处。此气无不在。理不变时。此气亦不变。理不息时。此气亦不息。故动而生阳者。亦此气之所为也。静而生阴者。亦此气之所为也。是岂可以有局有变之形气同看也哉。大抵有形之气。固有往者过来者续。而来者续时。已往之气。已无所在。无形之神气亦然乎。恨未及取质于栗谷门下也。○栗谷所谓本然之气。与愚见有同处焉。有异处焉。所谓同者。如栗谷与牛溪论四七书中所云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者是也。所谓异者。如今贤之所引非若理之于万物。本然之妙。无乎不在者是也。窃尝究其所以异者。盖吾儒之说气。有欠细腻。自古论气质者。徒知血气之流行者为气。形质之局定者为质。而不知血气亦属质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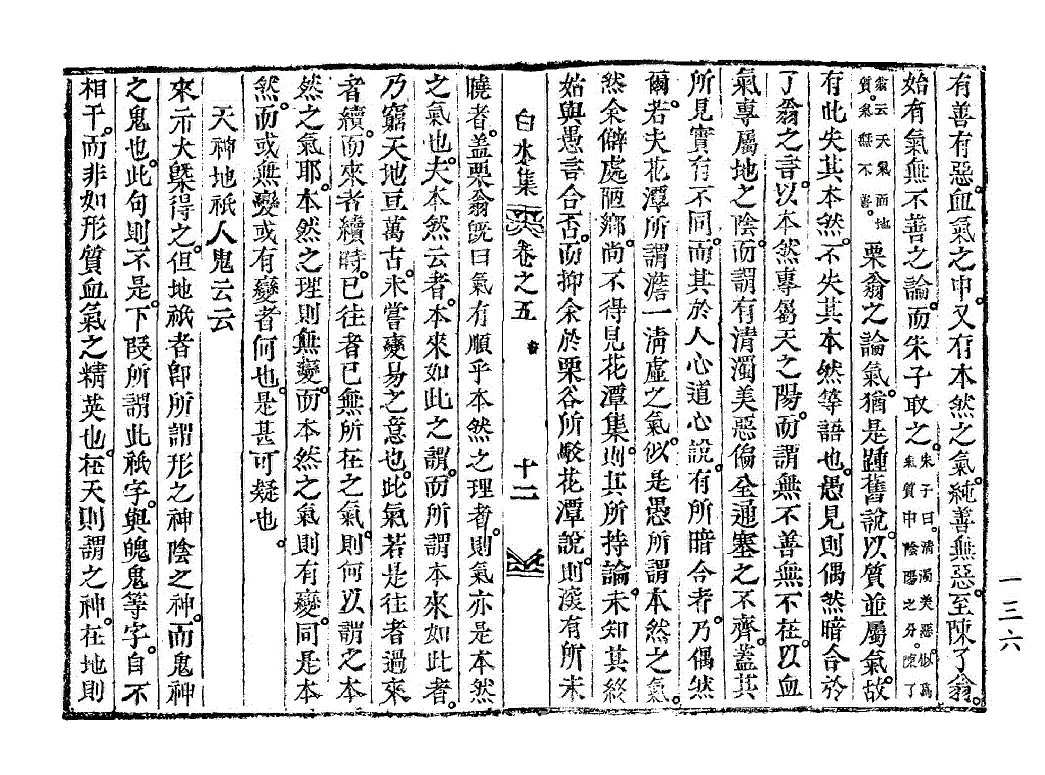 有善有恶。血气之中。又有本然之气。纯善无恶。至陈了翁。始有气无不善之论。而朱子取之。(朱子曰。清浊美恶。似为气质中阴阳之分。陈了翁云天气而地质。气无不善。)栗翁之论气。犹是踵旧说。以质并属气。故有此失其本然。不失其本然等语也。愚见则偶然暗合于了翁之言。以本然专属天之阳。而谓无不善无不在。以血气专属地之阴。而谓有清浊美恶偏全通塞之不齐。盖其所见实有不同。而其于人心道心说。有所暗合者。乃偶然尔。若夫花潭所谓澹一清虚之气。似是愚所谓本然之气。然余僻处陋乡。尚不得见花潭集。则其所持论。未知其终姑与愚言合否。而抑余于栗谷所驳花潭说。则深有所未晓者。盖栗翁既曰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夫本然云者。本来如此之谓。而所谓本来如此者。乃穷天地亘万古。未尝变易之意也。此气若是往者过来者续。而来者续时。已往者已无所在之气。则何以谓之本然之气耶。本然之理则无变。而本然之气则有变。同是本然。而或无变或有变者何也。是甚可疑也。
有善有恶。血气之中。又有本然之气。纯善无恶。至陈了翁。始有气无不善之论。而朱子取之。(朱子曰。清浊美恶。似为气质中阴阳之分。陈了翁云天气而地质。气无不善。)栗翁之论气。犹是踵旧说。以质并属气。故有此失其本然。不失其本然等语也。愚见则偶然暗合于了翁之言。以本然专属天之阳。而谓无不善无不在。以血气专属地之阴。而谓有清浊美恶偏全通塞之不齐。盖其所见实有不同。而其于人心道心说。有所暗合者。乃偶然尔。若夫花潭所谓澹一清虚之气。似是愚所谓本然之气。然余僻处陋乡。尚不得见花潭集。则其所持论。未知其终姑与愚言合否。而抑余于栗谷所驳花潭说。则深有所未晓者。盖栗翁既曰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夫本然云者。本来如此之谓。而所谓本来如此者。乃穷天地亘万古。未尝变易之意也。此气若是往者过来者续。而来者续时。已往者已无所在之气。则何以谓之本然之气耶。本然之理则无变。而本然之气则有变。同是本然。而或无变或有变者何也。是甚可疑也。天神地祇人鬼云云
来示大槩得之。但地祇者即所谓形之神阴之神。而鬼神之鬼也。此句则不是。下段所谓此祇字。与魄鬼等字。自不相干。而非如形质血气之精英也。在天则谓之神。在地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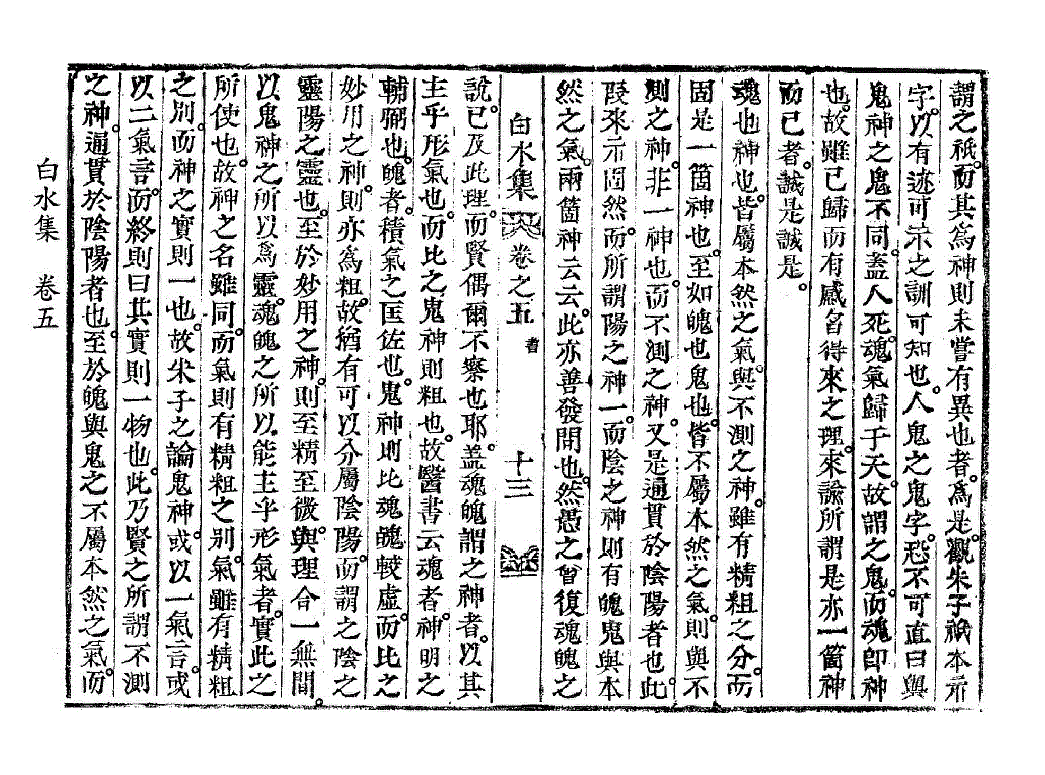 谓之祇。而其为神则未尝有异也者。为是。观朱子祇本示字。以有迹可示之训可知也。人鬼之鬼字。恐不可直曰与鬼神之鬼不同。盖人死。魂气归于天。故谓之鬼。而魂即神也。故虽已归而有感召得来之理。来谕所谓是亦一个神而已者。诚是诚是。
谓之祇。而其为神则未尝有异也者。为是。观朱子祇本示字。以有迹可示之训可知也。人鬼之鬼字。恐不可直曰与鬼神之鬼不同。盖人死。魂气归于天。故谓之鬼。而魂即神也。故虽已归而有感召得来之理。来谕所谓是亦一个神而已者。诚是诚是。魂也神也。皆属本然之气。与不测之神。虽有精粗之分。而固是一个神也。至如魄也鬼也。皆不属本然之气。则与不测之神。非一神也。而不测之神。又是通贯于阴阳者也。此段来示固然。而所谓阳之神一。而阴之神则有魄鬼与本然之气。两个神云云。此亦善发问也。然愚之曾复魂魄之说。已及此理。而贤偶尔不察也耶。盖魂魄谓之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而比之鬼神则粗也。故医书云魂者。神明之辅弼也。魄者。积气之匡佐也。鬼神则比魂魄较虚。而比之妙用之神。则亦为粗。故犹有可以分属阴阳。而谓之阴之灵阳之灵也。至于妙用之神。则至精至微。与理合一无间。以鬼神之所以为灵。魂魄之所以能主乎形气者。实此之所使也。故神之名虽同。而气则有精粗之别。气虽有精粗之别。而神之实则一也。故朱子之论鬼神。或以一气言。或以二气言。而终则曰其实则一物也。此乃贤之所谓不测之神。通贯于阴阳者也。至于魄与鬼之不属本然之气。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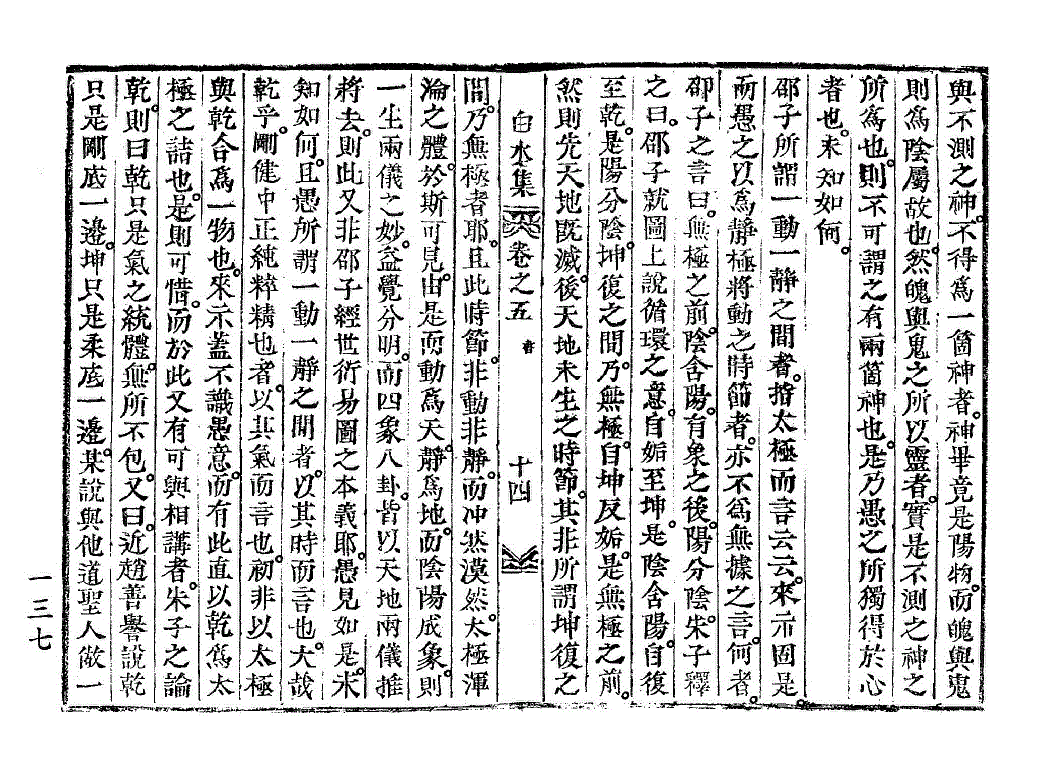 与不测之神。不得为一个神者。神毕竟是阳物。而魄与鬼则为阴属故也。然魄与鬼之所以灵者。实是不测之神之所为也。则不可谓之有两个神也。是乃愚之所独得于心者也。未知如何。
与不测之神。不得为一个神者。神毕竟是阳物。而魄与鬼则为阴属故也。然魄与鬼之所以灵者。实是不测之神之所为也。则不可谓之有两个神也。是乃愚之所独得于心者也。未知如何。邵子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指太极而言云云。来示固是。而愚之以为静极将动之时节者。亦不为无据之言。何者。邵子之言曰。无极之前。阴含阳。有象之后。阳分阴。朱子释之曰。邵子就图上说循环之意。自姤至坤。是阴含阳。自复至乾。是阳分阴。坤复之间。乃无极。自坤反姤。是无极之前。然则先天地既灭。后天地未生之时节。其非所谓坤复之间。乃无极者耶。且此时节。非动非静。而冲然漠然。太极浑沦之体。于斯可见。由是而动为天。静为地。而阴阳成象。则一生两仪之妙。益觉分明。而四象八卦。皆以天地两仪推将去。则此又非邵子经世衍易图之本义耶。愚见如是。未知如何。且愚所谓一动一静之间者。以其时而言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者。以其气而言也。初非以太极与乾合为一物也。来示盖不识愚意。而有此直以乾为太极之诘也。是则可惜。而于此又有可与相讲者。朱子之论乾。则曰乾只是气之统体。无所不包。又曰。近赵善誉说乾只是刚底一边。坤只是柔底一边。某说与他道圣人做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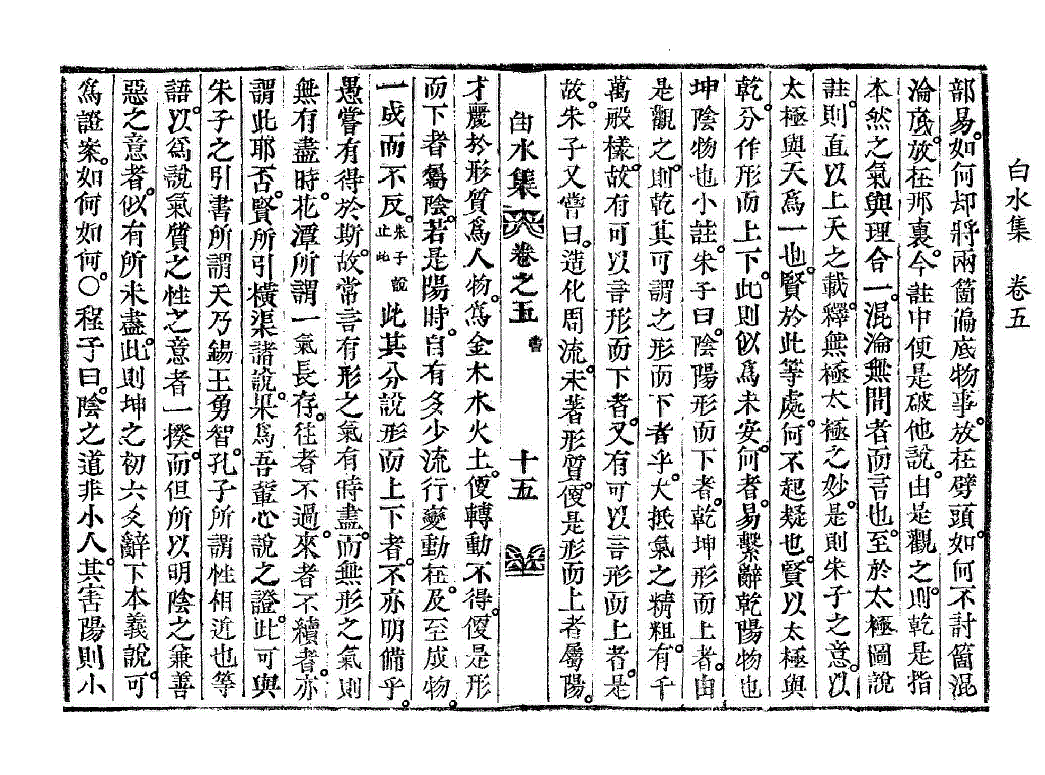 部易。如何却将两个偏底物事。放在劈头。如何不讨个混沦底。放在那里。今注中便是破他说。由是观之。则乾是指本然之气与理合一。混沦无间者而言也。至于太极图说注。则直以上天之载。释无极太极之妙。是则朱子之意。以太极与天为一也。贤于此等处。何不起疑也。贤以太极与乾。分作形而上下。此则似为未安。何者。易系辞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小注。朱子曰。阴阳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由是观之。则乾其可谓之形而下者乎。大抵气之精粗。有千万般样。故有可以言形而下者。又有可以言形而上者。是故。朱子又尝曰。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反。(朱子说止此)此其分说形而上下者。不亦明备乎。愚尝有得于斯。故常言有形之气有时尽。而无形之气则无有尽时。花潭所谓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者。亦谓此耶否。贤所引横渠诸说。果为吾辈心说之證。此可与朱子之引书所谓天乃锡王勇智。孔子所谓性相近也等语。以为说气质之性之意者一揆。而但所以明阴之兼善恶之意者。似有所未尽。此则坤之初六爻辞下本义说。可为證案。如何如何。○程子曰。阴之道非小人。其害阳则小
部易。如何却将两个偏底物事。放在劈头。如何不讨个混沦底。放在那里。今注中便是破他说。由是观之。则乾是指本然之气与理合一。混沦无间者而言也。至于太极图说注。则直以上天之载。释无极太极之妙。是则朱子之意。以太极与天为一也。贤于此等处。何不起疑也。贤以太极与乾。分作形而上下。此则似为未安。何者。易系辞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小注。朱子曰。阴阳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由是观之。则乾其可谓之形而下者乎。大抵气之精粗。有千万般样。故有可以言形而下者。又有可以言形而上者。是故。朱子又尝曰。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便是形而上者属阳。才丽于形质为人物。为金木水火土。便转动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属阴。若是阳时。自有多少流行变动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反。(朱子说止此)此其分说形而上下者。不亦明备乎。愚尝有得于斯。故常言有形之气有时尽。而无形之气则无有尽时。花潭所谓一气长存。往者不过。来者不续者。亦谓此耶否。贤所引横渠诸说。果为吾辈心说之證。此可与朱子之引书所谓天乃锡王勇智。孔子所谓性相近也等语。以为说气质之性之意者一揆。而但所以明阴之兼善恶之意者。似有所未尽。此则坤之初六爻辞下本义说。可为證案。如何如何。○程子曰。阴之道非小人。其害阳则小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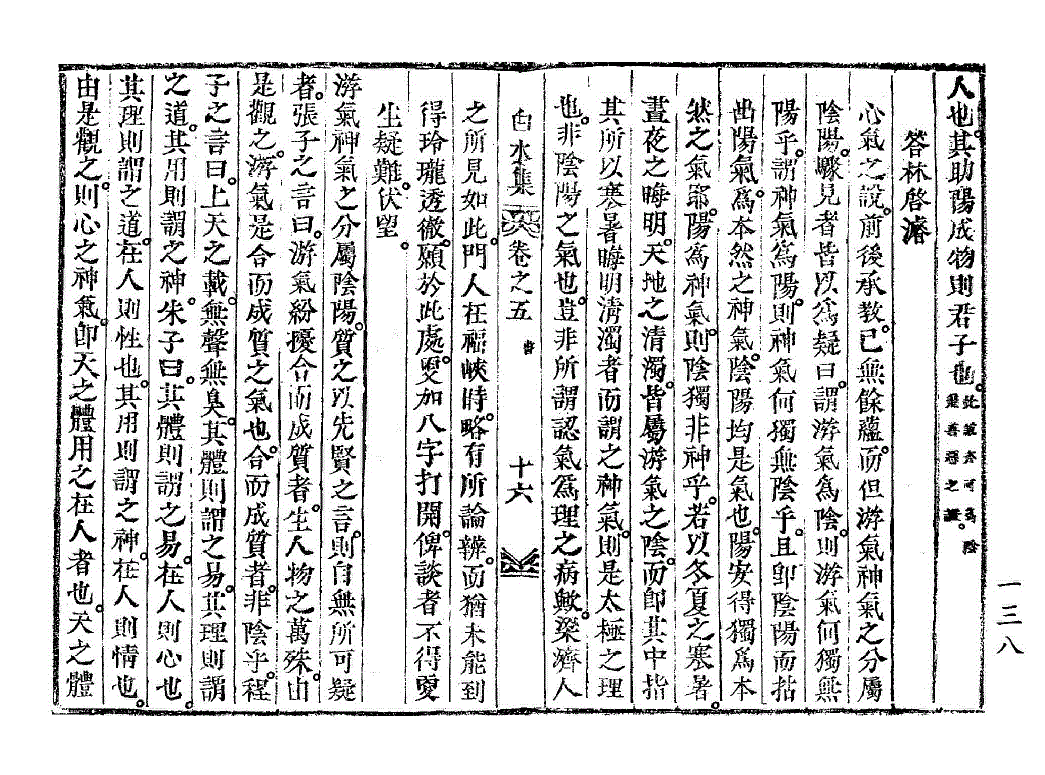 人也。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此说亦可为阴兼善恶之證。)
人也。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此说亦可为阴兼善恶之證。)答林启浚
心气之说。前后承教。已无馀蕴。而但游气神气之分属阴阳。骤见者皆以为疑曰。谓游气为阴。则游气何独无阳乎。谓神气为阳。则神气何独无阴乎。且即阴阳而拈出阳气。为本然之神气。阴阳均是气也。阳安得独为本然之气耶。阳为神气。则阴独非神乎。若以冬夏之寒暑。昼夜之晦明。天地之清浊。皆属游气之阴。而即其中指其所以寒暑晦明清浊者而谓之神气。则是太极之理也。非阴阳之气也。岂非所谓认气为理之病欤。梁济人之所见如此。门人在福峡时。略有所论辨。而犹未能到得玲珑透彻。愿于此处。更加八字打开。俾谈者不得更生疑难。伏望。
游气神气之分属阴阳。质之以先贤之言。则自无所可疑者。张子之言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由是观之。游气是合而成质之气也。合而成质者。非阴乎。程子之言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朱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理则谓之道。在人则性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由是观之。则心之神气。即天之体用之在人者也。天之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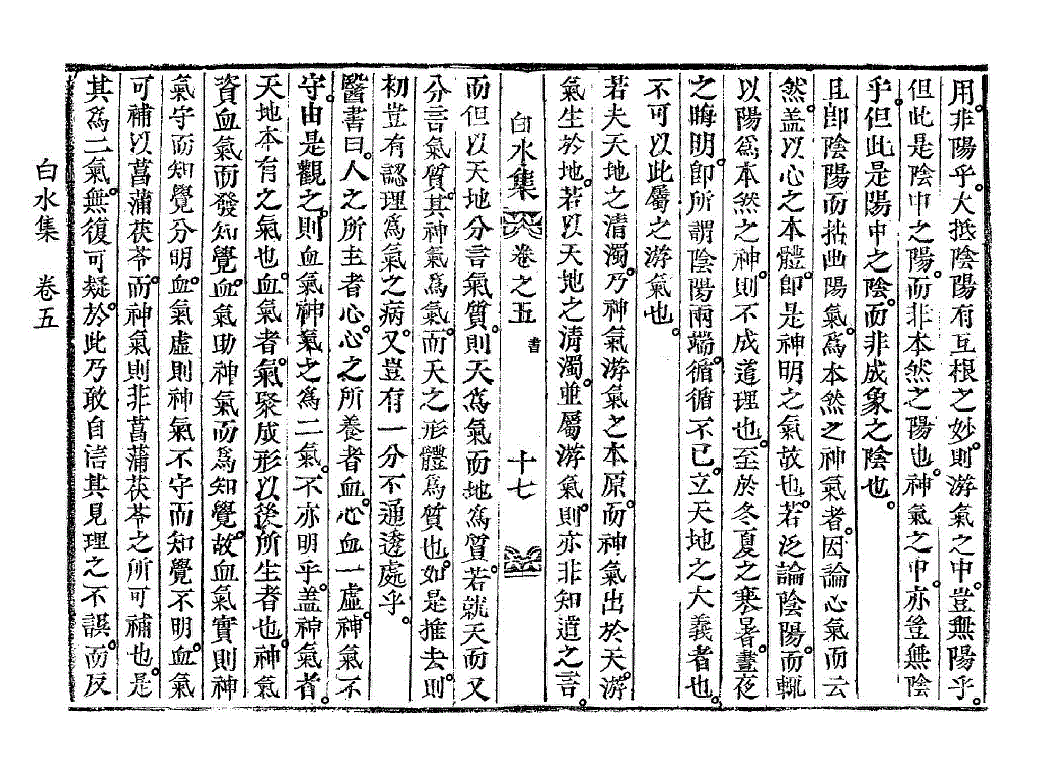 用。非阳乎。大抵阴阳有互根之妙。则游气之中。岂无阳乎。但此是阴中之阳。而非本然之阳也。神气之中。亦岂无阴乎。但此是阳中之阴。而非成象之阴也。
用。非阳乎。大抵阴阳有互根之妙。则游气之中。岂无阳乎。但此是阴中之阳。而非本然之阳也。神气之中。亦岂无阴乎。但此是阳中之阴。而非成象之阴也。且即阴阳而拈出阳气。为本然之神气者。因论心气而云然。盖以心之本体。即是神明之气故也。若泛论阴阳。而辄以阳为本然之神。则不成道理也。至于冬夏之寒暑。昼夜之晦明。即所谓阴阳两端。循循不已。立天地之大义者也。不可以此属之游气也。
若夫天地之清浊。乃神气游气之本原。而神气出于天。游气生于地。若以天地之清浊。并属游气。则亦非知道之言。而但以天地分言气质。则天为气而地为质。若就天而又分言气质。其神气为气。而天之形体为质也。如是推去。则初岂有认理为气之病。又岂有一分不通透处乎。
医书曰。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由是观之。则血气神气之为二气。不亦明乎。盖神气者。天地本有之气也。血气者。气聚成形以后所生者也。神气资血气而发知觉。血气助神气而为知觉。故血气实则神气守而知觉分明。血气虚则神气不守而知觉不明。血气可补以菖蒲茯苓。而神气则非菖蒲茯苓之所可补也。是其为二气。无复可疑。于此乃敢自信其见理之不误。而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3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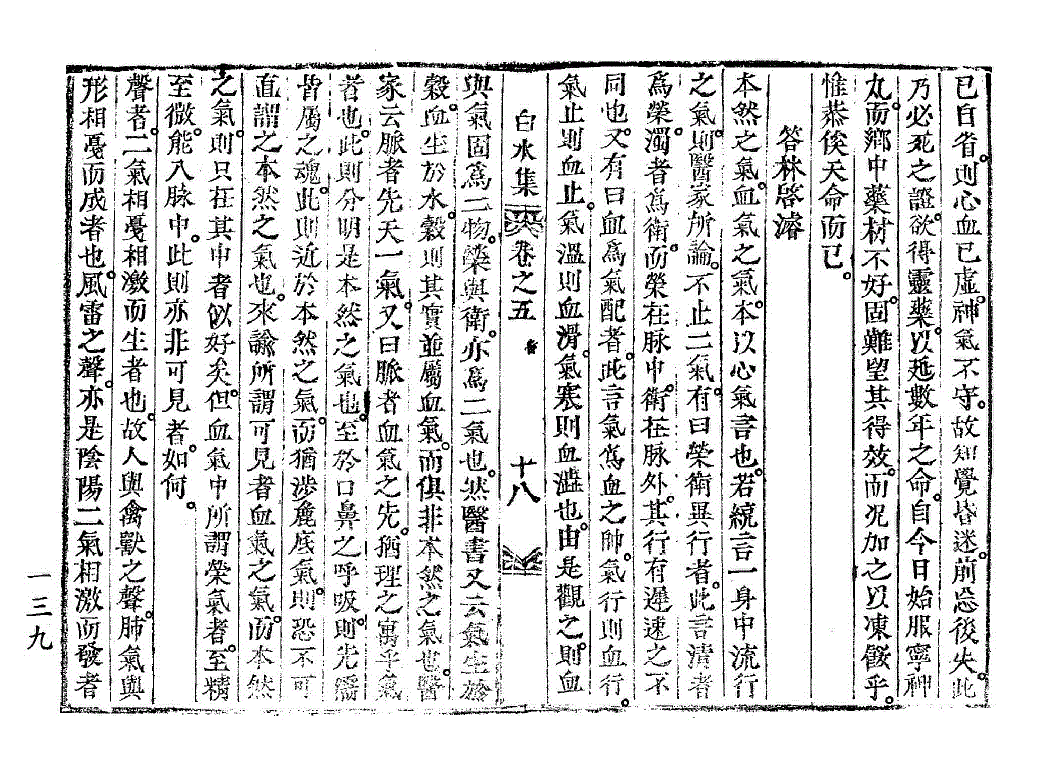 己自省。则心血已虚。神气不守。故知觉昏迷。前忘后失。此乃必死之證。欲得灵药。以延数年之命。自今日始服宁神丸。而乡中药材不好。固难望其得效。而况加之以冻馁乎。惟恭俟天命而已。
己自省。则心血已虚。神气不守。故知觉昏迷。前忘后失。此乃必死之證。欲得灵药。以延数年之命。自今日始服宁神丸。而乡中药材不好。固难望其得效。而况加之以冻馁乎。惟恭俟天命而已。答林启浚
本然之气。血气之气。本以心气言也。若统言一身中流行之气。则医家所论。不止二气。有曰荣卫异行者。此言清者为荣。浊者为卫。而荣在脉中。卫在脉外。其行有迟速之不同也。又有曰血为气配者。此言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涩也。由是观之。则血与气固为二物。荣与卫。亦为二气也。然医书又云气生于谷。血生于水。谷则其实并属血气。而俱非本然之气也。医家云脉者先天一气。又曰脉者血气之先。犹理之寓乎气者也。此则分明是本然之气也。至于口鼻之呼吸。则先儒皆属之魂。此则近于本然之气。而犹涉粗底气。则恐不可直谓之本然之气也。来谕所谓可见者血气之气。而本然之气。则只在其中者似好矣。但血气中所谓荣气者。至精至微。能入脉中。此则亦非可见者。如何。
声者。二气相戛相激而生者也。故人与禽兽之声。肺气与形相戛而成者也。风雷之声。亦是阴阳二气相激而发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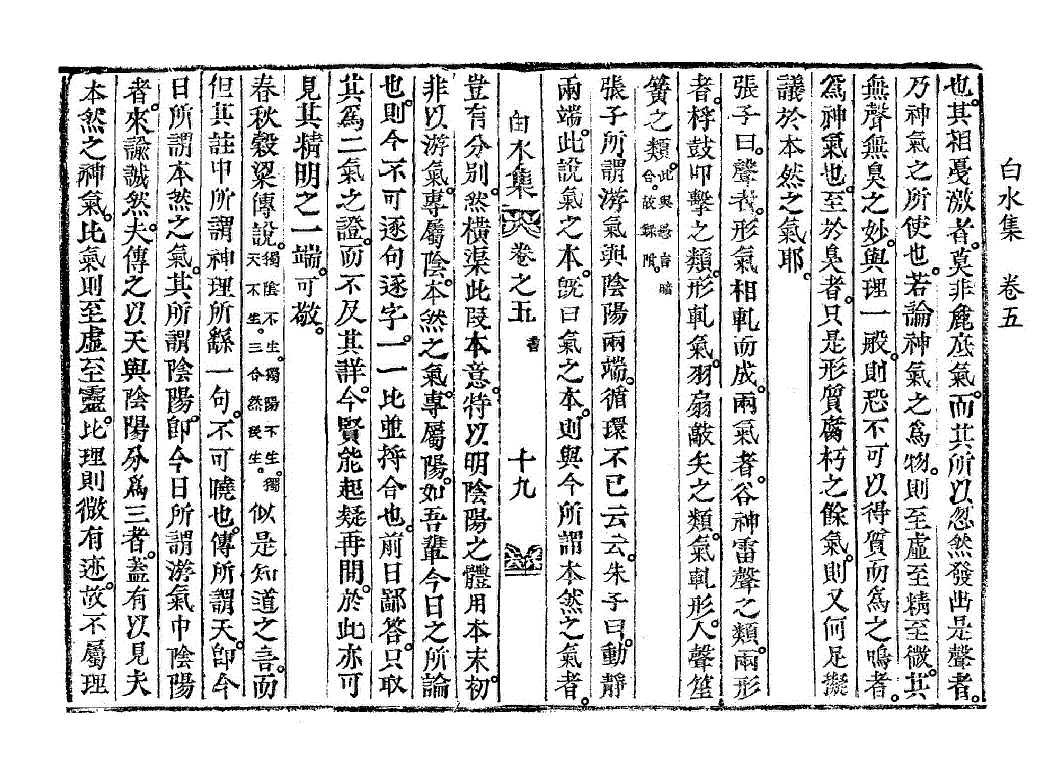 也。其相戛激者。莫非粗底气。而其所以忽然发出是声者。乃神气之所使也。若论神气之为物。则至虚至精至微。其无声无臭之妙。与理一般。则恐不可以得质而为之鸣者。为神气也。至于臭者。只是形质腐朽之馀气。则又何足拟议于本然之气耶。
也。其相戛激者。莫非粗底气。而其所以忽然发出是声者。乃神气之所使也。若论神气之为物。则至虚至精至微。其无声无臭之妙。与理一般。则恐不可以得质而为之鸣者。为神气也。至于臭者。只是形质腐朽之馀气。则又何足拟议于本然之气耶。张子曰。声者。形气相轧而成。两气者。谷神雷声之类。两形者。桴鼓叩击之类。形轧气。羽扇敲矢之类。气轧形。人声笙簧之类。(此与愚言暗合。故录附。)
张子所谓游气与阴阳两端。循环不已云云。朱子曰。动静两端。此说气之本。既曰气之本。则与今所谓本然之气者。岂有分别。然横渠此段本意。特以明阴阳之体用本末。初非以游气。专属阴。本然之气。专属阳。如吾辈今日之所论也。则今不可逐句逐字。一一比并捋合也。前日鄙答。只取其为二气之證。而不及其详。今贤能起疑再问。于此亦可见其精明之一端。可敬。
春秋谷粱传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似是知道之言。而但其注中所谓神理所繇一句。不可晓也。传所谓天。即今日所谓本然之气。其所谓阴阳。即今日所谓游气中阴阳者。来谕诚然。夫传之以天与阴阳分为三者。盖有以见夫本然之神气。比气则至虚至灵。比理则微有迹。故不属理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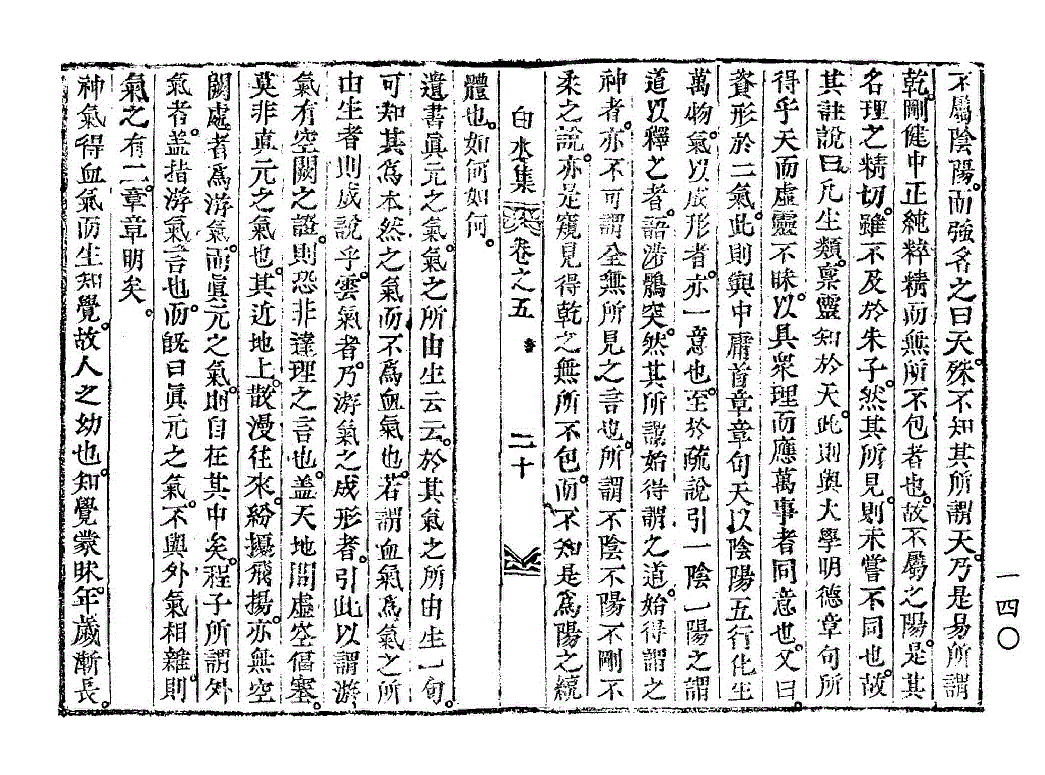 不属阴阳。而强名之曰天。殊不知其所谓天。乃是易所谓乾。刚健中正纯粹精而无所不包者也。故不属之阳。是其名理之精切。虽不及于朱子。然其所见。则未尝不同也。故其注说曰。凡生类。禀灵知于天。此则与大学明德章句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同意也。又曰。资形于二气。此则与中庸首章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者。亦一意也。至于疏说引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释之者。语涉鹘突。然其所谓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者。亦不可谓全无所见之言也。所谓不阴不阳不刚不柔之说。亦是窥见得乾之无所不包。而不知是为阳之统体也。如何如何。
不属阴阳。而强名之曰天。殊不知其所谓天。乃是易所谓乾。刚健中正纯粹精而无所不包者也。故不属之阳。是其名理之精切。虽不及于朱子。然其所见。则未尝不同也。故其注说曰。凡生类。禀灵知于天。此则与大学明德章句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同意也。又曰。资形于二气。此则与中庸首章章句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者。亦一意也。至于疏说引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释之者。语涉鹘突。然其所谓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者。亦不可谓全无所见之言也。所谓不阴不阳不刚不柔之说。亦是窥见得乾之无所不包。而不知是为阳之统体也。如何如何。遗书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云云。于其气之所由生一句。可知其为本然之气而不为血气也。若谓血气为气之所由生者则成说乎。云气者。乃游气之成形者。引此以谓游气有空阙之證。则恐非达理之言也。盖天地间虚空偪塞。莫非真元之气也。其近地上。散漫往来。纷扰飞扬。亦无空阙处者为游气。而真元之气。则自在其中矣。程子所谓外气者。盖指游气言也。而既曰真元之气。不与外气相杂。则气之有二。章章明矣。
神气得血气而生知觉。故人之幼也。知觉蒙昧。年岁渐长。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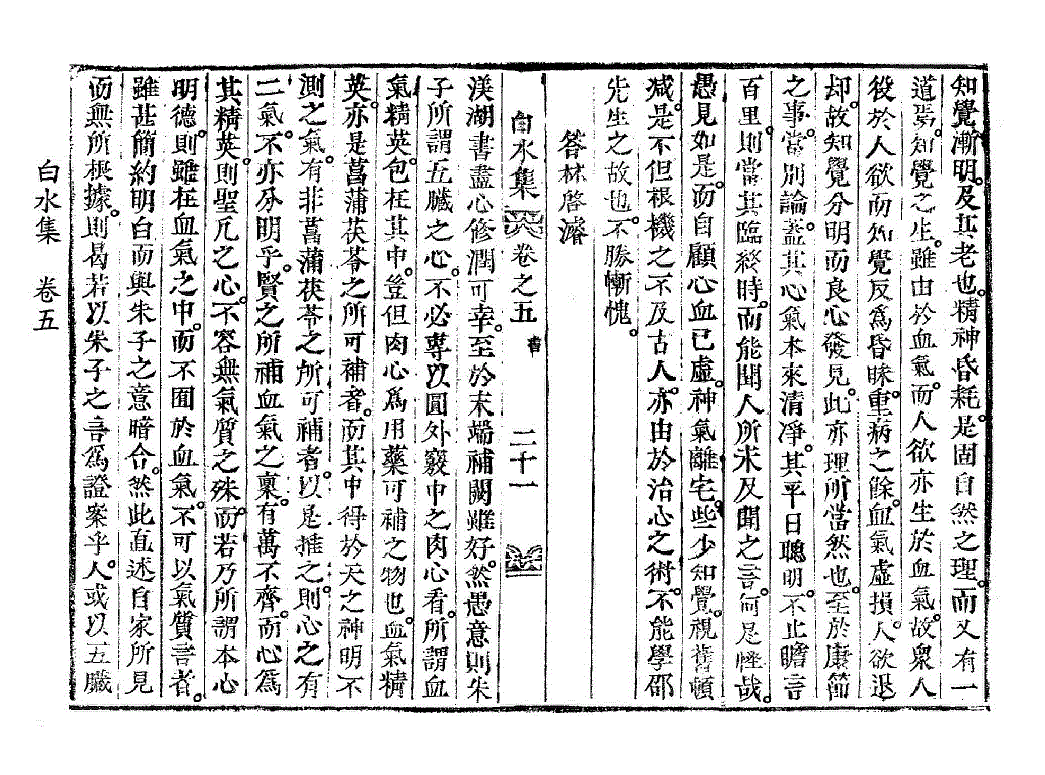 知觉渐明。及其老也。精神昏耗。是固自然之理。而又有一道焉。知觉之生。虽由于血气。而人欲亦生于血气。故众人役于人欲而知觉反为昏昧。重病之馀。血气虚损。人欲退却。故知觉分明而良心发见。此亦理所当然也。至于康节之事。当别论。盖其心气本来清净。其平日聪明。不止瞻言百里。则当其临终时。而能闻人所未及闻之言。何足怪哉。愚见如是。而自顾心血已虚。神气离宅。些少知觉。视旧顿减。是不但根机之不及古人。亦由于治心之术。不能学邵先生之故也。不胜惭愧。
知觉渐明。及其老也。精神昏耗。是固自然之理。而又有一道焉。知觉之生。虽由于血气。而人欲亦生于血气。故众人役于人欲而知觉反为昏昧。重病之馀。血气虚损。人欲退却。故知觉分明而良心发见。此亦理所当然也。至于康节之事。当别论。盖其心气本来清净。其平日聪明。不止瞻言百里。则当其临终时。而能闻人所未及闻之言。何足怪哉。愚见如是。而自顾心血已虚。神气离宅。些少知觉。视旧顿减。是不但根机之不及古人。亦由于治心之术。不能学邵先生之故也。不胜惭愧。答林启浚
渼湖书尽心修润可幸。至于末端补阙虽好。然愚意则朱子所谓五脏之心。不必专以圆外窍中之肉心看。所谓血气精英。包在其中。岂但肉心为用药可补之物也。血气精英。亦是菖蒲茯苓之所可补者。而其中得于天之神明不测之气。有非菖蒲茯苓之所可补者。以是推之。则心之有二气。不亦分明乎。贤之所补血气之禀。有万不齐。而心为其精英。则圣凡之心。不容无气质之殊。而若乃所谓本心明德。则虽在血气之中。而不囿于血气。不可以气质言者。虽甚简约明白而与朱子之意暗合。然此直述自家所见而无所根据。则曷若以朱子之言为證案乎。人或以五脏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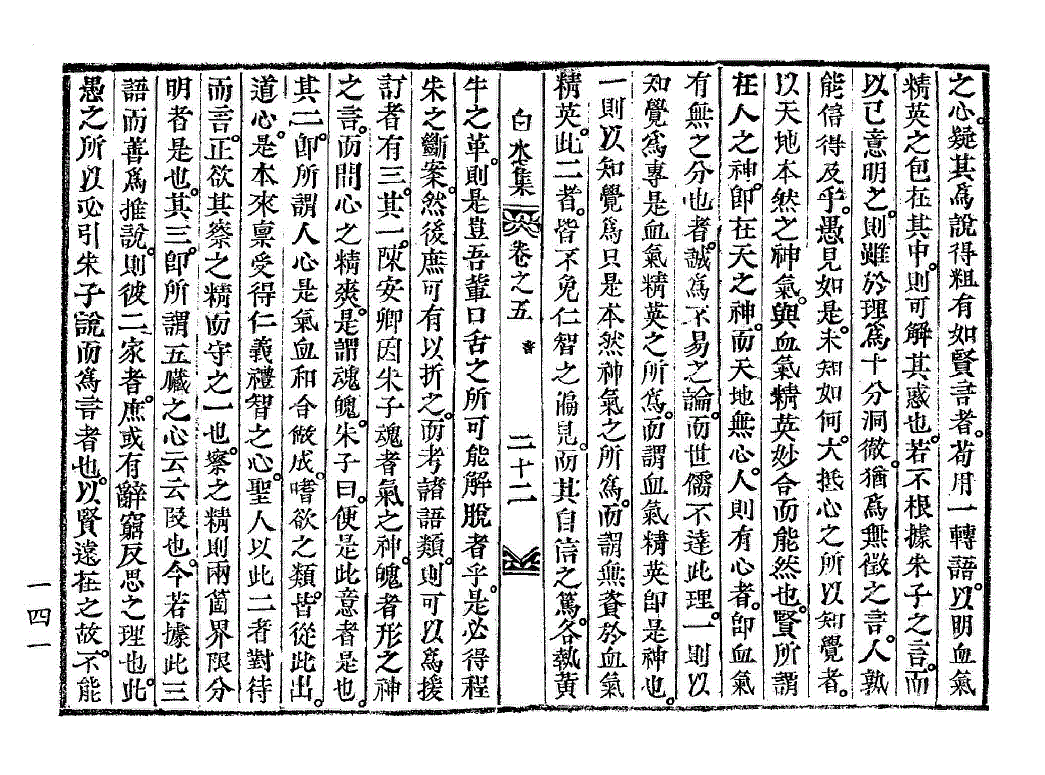 之心。疑其为说得粗有如贤言者。苟用一转语。以明血气精英之包在其中。则可解其惑也。若不根据朱子之言。而以己意明之。则虽于理为十分洞彻。犹为无徵之言。人孰能信得及乎。愚见如是。未知如何。大抵心之所以知觉者。以天地本然之神气。与血气精英妙合而能然也。贤所谓在人之神。即在天之神。而天地无心。人则有心者。即血气有无之分也者。诚为不易之论。而世儒不达此理。一则以知觉为专是血气精英之所为。而谓血气精英即是神也。一则以知觉为只是本然神气之所为。而谓无资于血气精英。此二者。皆不免仁智之偏见。而其自信之笃。各执黄牛之革。则是岂吾辈口舌之所可能解脱者乎。是必得程朱之断案。然后庶可有以折之。而考诸语类。则可以为援订者有三。其一。陈安卿因朱子魂者气之神。魄者形之神之言。而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朱子曰。便是此意者是也。其二。即所谓人心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者是也。其三。即所谓五脏之心云云段也。今若据此三语而善为推说。则彼二家者。庶或有辞穷反思之理也。此愚之所以必引朱子说而为言者也。以贤远在之故。不能
之心。疑其为说得粗有如贤言者。苟用一转语。以明血气精英之包在其中。则可解其惑也。若不根据朱子之言。而以己意明之。则虽于理为十分洞彻。犹为无徵之言。人孰能信得及乎。愚见如是。未知如何。大抵心之所以知觉者。以天地本然之神气。与血气精英妙合而能然也。贤所谓在人之神。即在天之神。而天地无心。人则有心者。即血气有无之分也者。诚为不易之论。而世儒不达此理。一则以知觉为专是血气精英之所为。而谓血气精英即是神也。一则以知觉为只是本然神气之所为。而谓无资于血气精英。此二者。皆不免仁智之偏见。而其自信之笃。各执黄牛之革。则是岂吾辈口舌之所可能解脱者乎。是必得程朱之断案。然后庶可有以折之。而考诸语类。则可以为援订者有三。其一。陈安卿因朱子魂者气之神。魄者形之神之言。而问心之精爽。是谓魂魄。朱子曰。便是此意者是也。其二。即所谓人心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者是也。其三。即所谓五脏之心云云段也。今若据此三语而善为推说。则彼二家者。庶或有辞穷反思之理也。此愚之所以必引朱子说而为言者也。以贤远在之故。不能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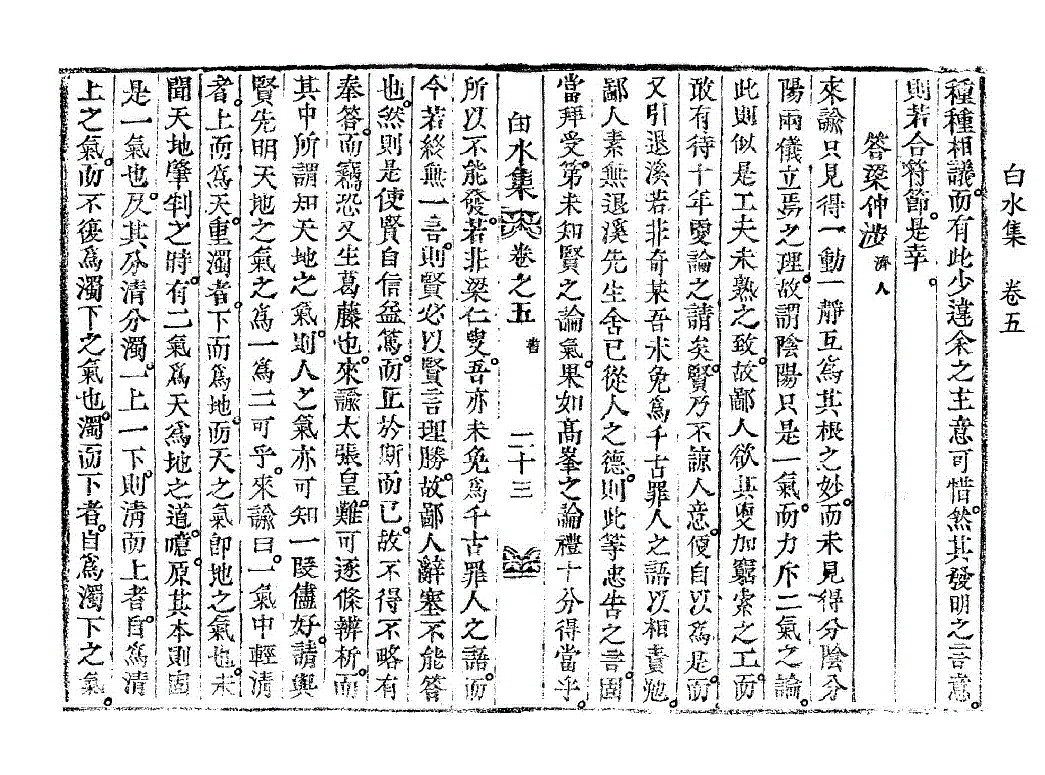 种种相议。而有此少违余之主意可惜。然其发明之言意。则若合符节。是幸。
种种相议。而有此少违余之主意可惜。然其发明之言意。则若合符节。是幸。答梁仲涉(济人)
来谕只见得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妙。而未见得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之理。故谓阴阳只是一气。而力斥二气之论。此则似是工夫未熟之致。故鄙人欲其更加穷索之工。而敢有待十年更论之请矣。贤乃不谅人意。便自以为是。而又引退溪若非奇某吾未免为千古罪人之语以相责勉。鄙人素无退溪先生舍己从人之德。则此等忠告之言。固当拜受。第未知贤之论气。果如高峰之论礼十分得当乎。所以不能发。若非梁仁叟。吾亦未免为千古罪人之语。而今若终无一言。则贤必以贤言理胜。故鄙人辞塞不能答也。然则是使贤自信益笃。而止于斯而已。故不得不略有奉答。而窃恐又生葛藤也。来谕太张皇。难可逐条辨析。而其中所谓知天地之气。则人之气亦可知一段尽好。请与贤先明天地之气之为一为二可乎。来谕曰。一气中轻清者。上而为天。重浊者。下而为地。而天之气即地之气也。未闻天地肇判之时。有二气为天为地之道。噫。原其本则固是一气也。及其分清分浊。一上一下。则清而上者。自为清上之气。而不复为浊下之气也。浊而下者。自为浊下之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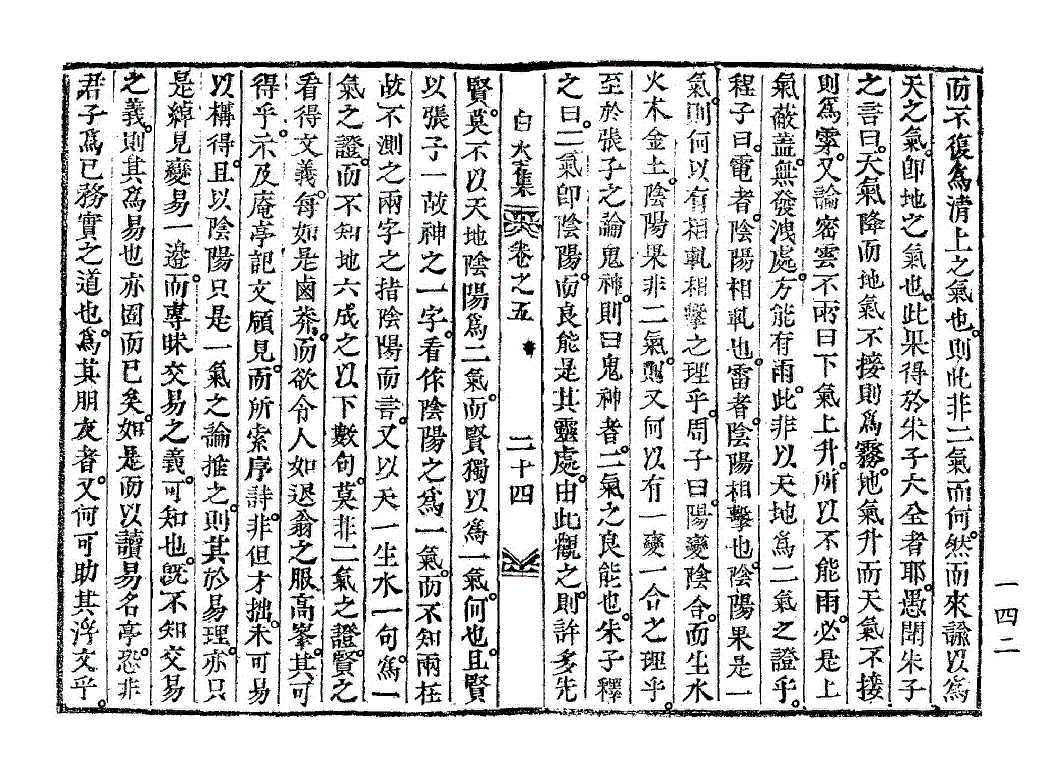 而不复为清上之气也。则此非二气而何。然而来谕以为天之气。即地之气也。此果得于朱子大全者耶。愚闻朱子之言曰。天气降而地气不接则为雾。地气升而天气不接则为雺。又论密云不两曰下气上升。所以不能雨。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此非以天地为二气之證乎。程子曰。电者。阴阳相轧也。雷者。阴阳相击也。阴阳果是一气。则何以有相轧相击之理乎。周子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果非二气。则又何以有一变一合之理乎。至于张子之论鬼神。则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朱子释之曰。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由此观之。则许多先贤。莫不以天地阴阳为二气。而贤独以为一气。何也。且贤以张子一故神之一字。看作阴阳之为一气。而不知两在故不测之两字之指阴阳而言。又以天一生水一句。为一气之證。而不知地六成之以下数句。莫非二气之證。贤之看得文义。每如是卤莽。而欲令人如退翁之服高峰。其可得乎。示及庵亭记文领见。而所索序诗。非但才拙。未可易以构得。且以阴阳只是一气之论推之。则其于易理。亦只是绰见变易一边。而专昧交易之义。可知也。既不知交易之义。则其为易也亦固而已矣。如是而以读易名亭。恐非君子为己务实之道也。为其朋友者。又何可助其浮文乎。
而不复为清上之气也。则此非二气而何。然而来谕以为天之气。即地之气也。此果得于朱子大全者耶。愚闻朱子之言曰。天气降而地气不接则为雾。地气升而天气不接则为雺。又论密云不两曰下气上升。所以不能雨。必是上气蔽盖。无发泄处。方能有雨。此非以天地为二气之證乎。程子曰。电者。阴阳相轧也。雷者。阴阳相击也。阴阳果是一气。则何以有相轧相击之理乎。周子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阴阳果非二气。则又何以有一变一合之理乎。至于张子之论鬼神。则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朱子释之曰。二气即阴阳。而良能是其灵处。由此观之。则许多先贤。莫不以天地阴阳为二气。而贤独以为一气。何也。且贤以张子一故神之一字。看作阴阳之为一气。而不知两在故不测之两字之指阴阳而言。又以天一生水一句。为一气之證。而不知地六成之以下数句。莫非二气之證。贤之看得文义。每如是卤莽。而欲令人如退翁之服高峰。其可得乎。示及庵亭记文领见。而所索序诗。非但才拙。未可易以构得。且以阴阳只是一气之论推之。则其于易理。亦只是绰见变易一边。而专昧交易之义。可知也。既不知交易之义。则其为易也亦固而已矣。如是而以读易名亭。恐非君子为己务实之道也。为其朋友者。又何可助其浮文乎。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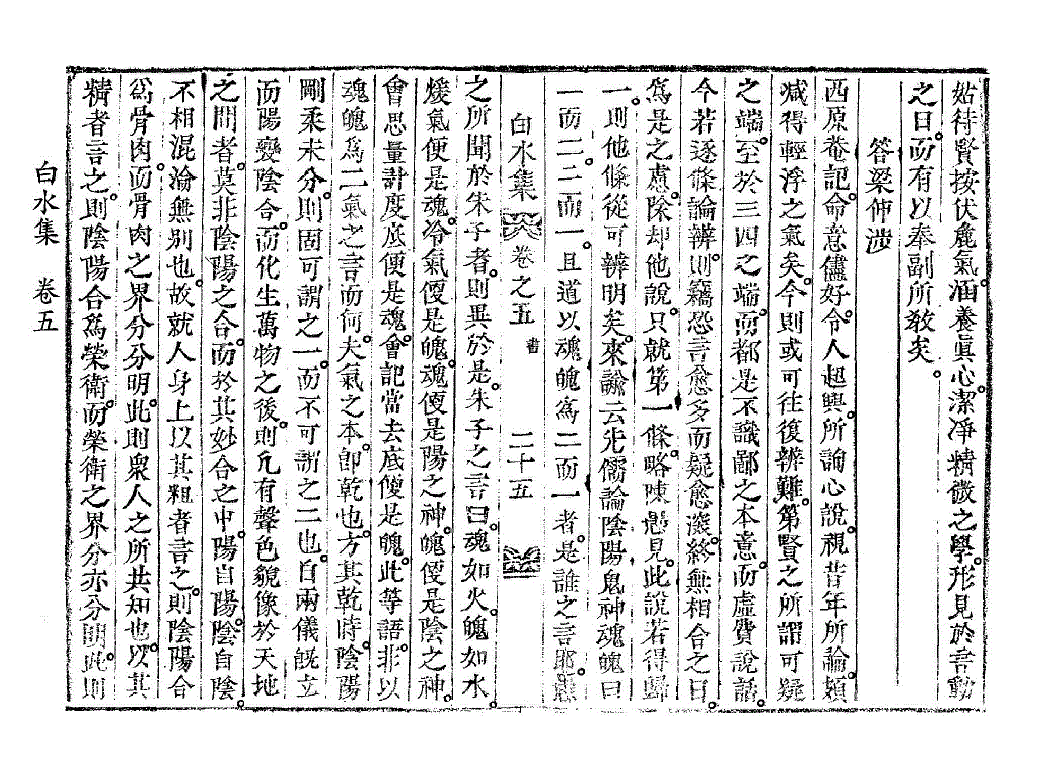 姑待贤按伏粗气。涵养真心。洁净精微之学。形见于言动之日。而有以奉副所教矣。
姑待贤按伏粗气。涵养真心。洁净精微之学。形见于言动之日。而有以奉副所教矣。答梁仲涉
西原庵记。命意尽好。令人起兴。所询心说。视昔年所论。颇减得轻浮之气矣。今则或可往复辨难。第贤之所谓可疑之端。至于三四之端。而都是不识鄙之本意。而虚费说话。今若逐条论辨。则窃恐言愈多而疑愈深。终无相合之日。为是之虑。除却他说。只就第一条。略陈愚见。此说若得归一。则他条从可辨明矣。来谕云先儒论阴阳鬼神魂魄曰一而二。二而一。且道以魂魄为二而一者。是谁之言耶。愚之所闻于朱子者。则异于是。朱子之言曰。魂如火。魄如水。煖气便是魂。冷气便是魄。魂便是阳之神。魄便是阴之神。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此等语。非以魂魄为二气之言而何。夫气之本。即乾也。方其乾时。阴阳刚柔未分。则固可谓之一。而不可谓之二也。自两仪既立而阳变阴合。而化生万物之后。则凡有声色貌像于天地之间者。莫非阴阳之合。而于其妙合之中。阳自阳。阴自阴。不相混沦无别也。故就人身上以其粗者言之。则阴阳合为骨肉。而骨肉之界分分明。此则众人之所共知也。以其精者言之。则阴阳合为荣卫。而荣卫之界分亦分明。此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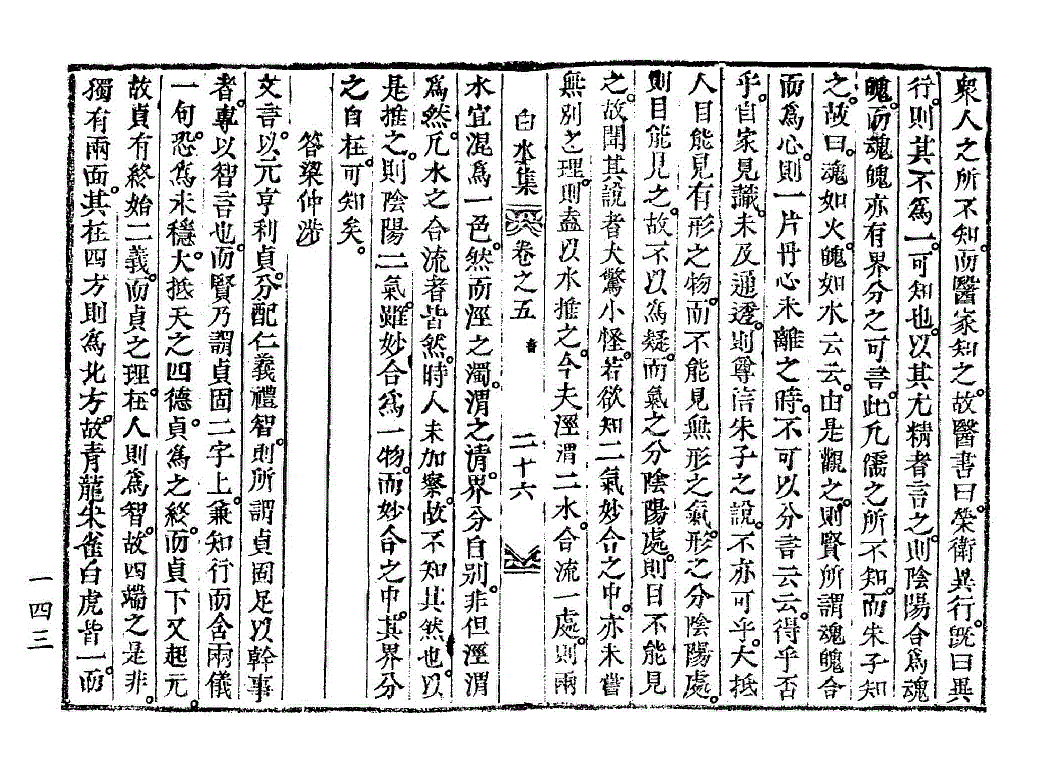 众人之所不知。而医家知之。故医书曰。荣卫异行。既曰异行。则其不为一。可知也。以其尤精者言之。则阴阳合为魂魄。而魂魄亦有界分之可言。此凡儒之所不知。而朱子知之。故曰。魂如火。魄如水云云。由是观之。则贤所谓魂魄合而为心。则一片丹心未离之时。不可以分言云云。得乎否乎。自家见识。未及通透。则尊信朱子之说。不亦可乎。大抵人目能见有形之物。而不能见无形之气。形之分阴阳处。则目能见之。故不以为疑。而气之分阴阳处。则目不能见之。故闻其说者大惊小怪。若欲知二气妙合之中。亦未尝无别之理。则盍以水推之。今夫泾渭二水。合流一处。则两水宜混为一色。然而泾之浊。渭之清。界分自别。非但泾渭为然。凡水之合流者皆然。时人未加察。故不知其然也。以是推之。则阴阳二气。虽妙合为一物。而妙合之中。其界分之自在。可知矣。
众人之所不知。而医家知之。故医书曰。荣卫异行。既曰异行。则其不为一。可知也。以其尤精者言之。则阴阳合为魂魄。而魂魄亦有界分之可言。此凡儒之所不知。而朱子知之。故曰。魂如火。魄如水云云。由是观之。则贤所谓魂魄合而为心。则一片丹心未离之时。不可以分言云云。得乎否乎。自家见识。未及通透。则尊信朱子之说。不亦可乎。大抵人目能见有形之物。而不能见无形之气。形之分阴阳处。则目能见之。故不以为疑。而气之分阴阳处。则目不能见之。故闻其说者大惊小怪。若欲知二气妙合之中。亦未尝无别之理。则盍以水推之。今夫泾渭二水。合流一处。则两水宜混为一色。然而泾之浊。渭之清。界分自别。非但泾渭为然。凡水之合流者皆然。时人未加察。故不知其然也。以是推之。则阴阳二气。虽妙合为一物。而妙合之中。其界分之自在。可知矣。答梁仲涉
文言。以元亨利贞。分配仁义礼智。则所谓贞固足以干事者。专以智言也。而贤乃谓贞固二字上。兼知行而含两仪一句。恐为未稳。大抵天之四德。贞为之终。而贞下又起元。故贞有终始二义。而贞之理。在人则为智。故四端之是非。独有两面。其在四方则为北方。故青龙,朱雀,白虎皆一。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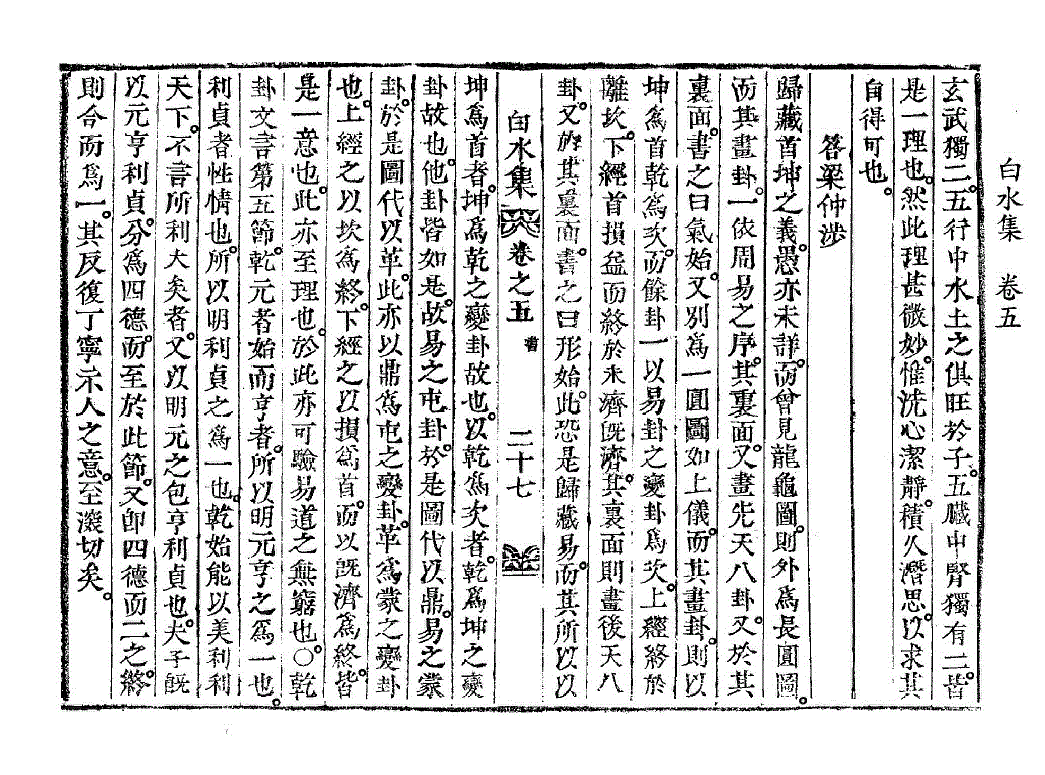 玄武独二。五行中水土之俱旺于子。五脏中肾独有二。皆是一理也。然此理甚微妙。惟洗心洁静。积久潜思。以求其自得可也。
玄武独二。五行中水土之俱旺于子。五脏中肾独有二。皆是一理也。然此理甚微妙。惟洗心洁静。积久潜思。以求其自得可也。答梁仲涉
归藏首坤之义。愚亦未详。而曾见龙龟图。则外为长圆图。而其画卦。一依周易之序。其里面。又画先天八卦。又于其里面。书之曰气始。又别为一圆图如上仪。而其画卦。则以坤为首乾为次。而馀卦一以易卦之变卦为次。上经终于离坎。下经首损益而终于未济既济。其里面则画后天八卦。又于其里面。书之曰形始。此恐是归藏易。而其所以以坤为首者。坤为乾之变卦故也。以乾为次者。乾为坤之变卦故也。他卦皆如是。故易之屯卦。于是图代以鼎。易之蒙卦。于是图代以革。此亦以鼎为屯之变卦。革为蒙之变卦也。上经之以坎为终。下经之以损为首。而以既济为终。皆是一意也。此亦至理也。于此亦可验易道之无穷也。○乾卦文言第五节。乾元者始而亨者。所以明元亨之为一也。利贞者性情也。所以明利贞之为一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者。又以明元之包亨利贞也。夫子既以元亨利贞。分为四德。而至于此节。又即四德而二之。终则合而为一。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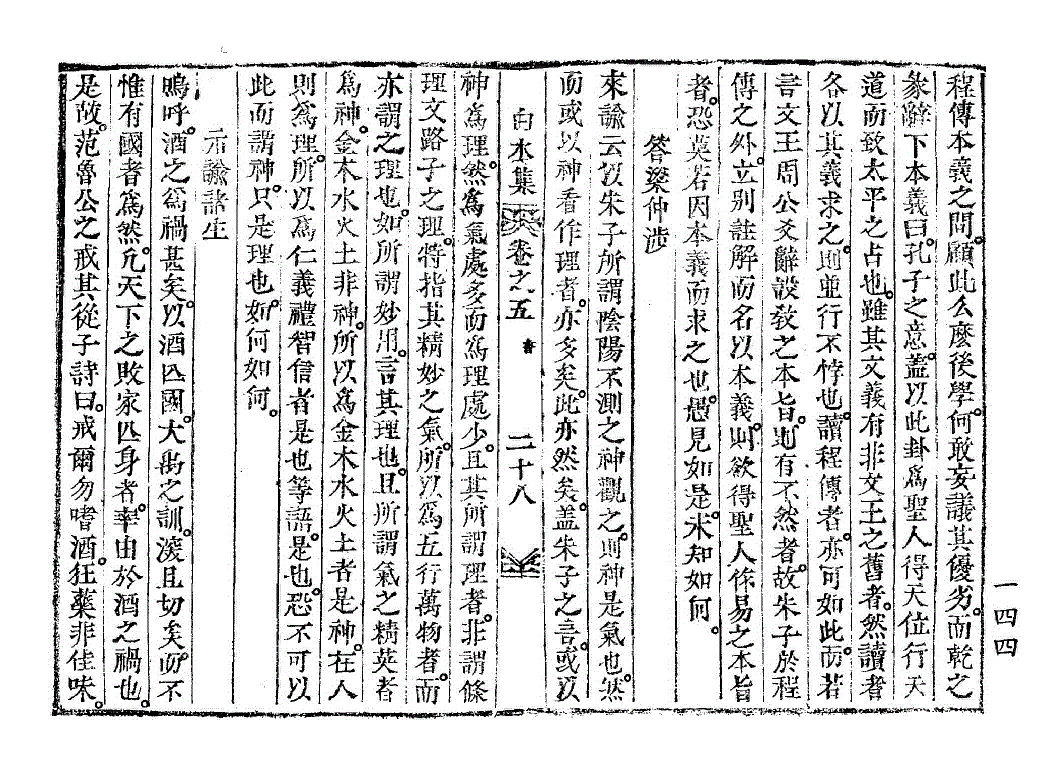 程传本义之问。顾此幺么后学。何敢妄议其优劣。而乾之彖辞下本义曰。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义求之。则并行不悖也。读程传者。亦可如此。而若言文王周公爻辞设教之本旨。则有不然者。故朱子于程传之外。立别注解而名以本义。则欲得圣人作易之本旨者。恐莫若因本义而求之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程传本义之问。顾此幺么后学。何敢妄议其优劣。而乾之彖辞下本义曰。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虽其文义有非文王之旧者。然读者各以其义求之。则并行不悖也。读程传者。亦可如此。而若言文王周公爻辞设教之本旨。则有不然者。故朱子于程传之外。立别注解而名以本义。则欲得圣人作易之本旨者。恐莫若因本义而求之也。愚见如是。未知如何。答梁仲涉
来谕云以朱子所谓阴阳不测之神观之。则神是气也。然而或以神看作理者。亦多矣。此亦然矣。盖朱子之言。或以神为理。然为气处多而为理处少。且其所谓理者。非谓条理文路子之理。特指其精妙之气。所以为五行万物者。而亦谓之理也。如所谓妙用。言其理也。且所谓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等语。是也。恐不可以此而谓神。只是理也。如何如何。
示谕诸生
呜呼。酒之为祸甚矣。以酒亡国。大禹之训。深且切矣。而不惟有国者为然。凡天下之败家亡身者。率由于酒之祸也。是故。范鲁公之戒其从子诗曰。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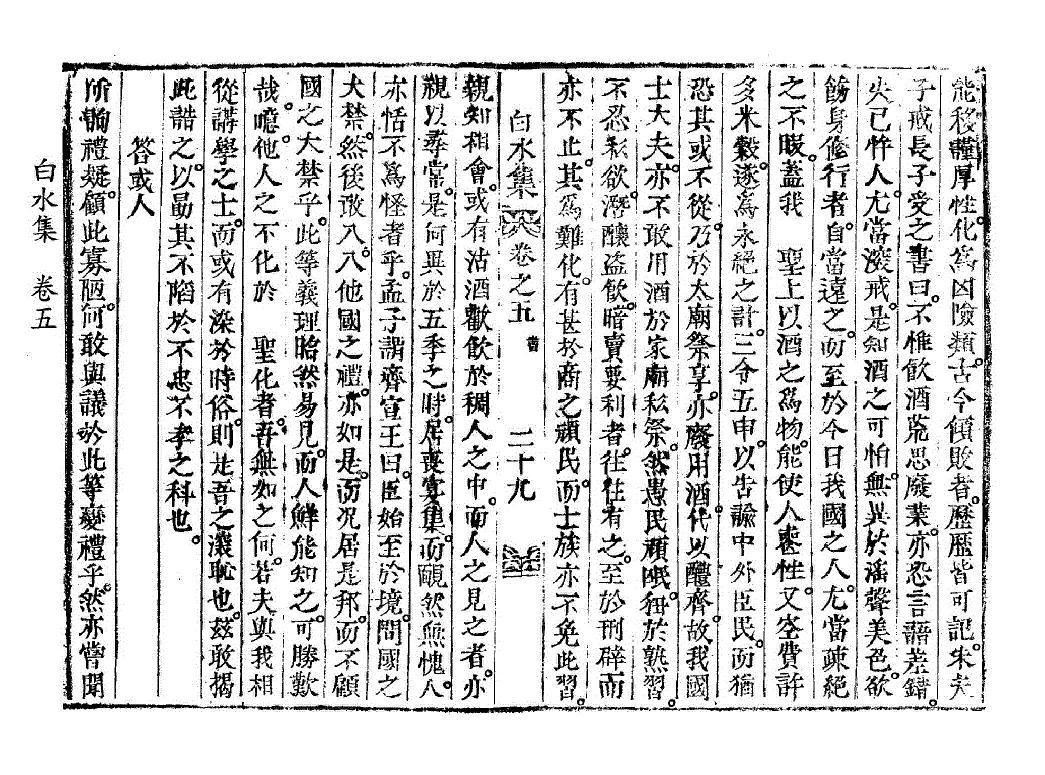 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朱夫子戒长子受之书曰。不惟饮酒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尤当深戒。是知酒之可怕。无异于淫声美色。欲饬身修行者。自当远之。而至于今日我国之人。尤当疏绝之不暇。盖我 圣上以酒之为物。能使人丧性。又空费许多米谷。遂为永绝之计。三令五申。以告谕中外臣民。而犹恐其或不从。乃于太庙祭享。亦废用酒。代以醴齐。故我国士大夫。亦不敢用酒于家庙私祭。然愚民顽氓。狃于熟习。不忍私欲。潜酿盗饮。暗卖要利者。往往有之。至于刑辟而亦不止。其为难化。有甚于商之顽民。而士族亦不免此习。亲知相会。或有沽酒欢饮于稠人之中。而人之见之者。亦视以寻常。是何异于五季之时。居丧宴集。而腼然无愧。人亦恬不为怪者乎。孟子谓齐宣王曰。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入他国之礼。亦如是。而况居是邦。而不顾国之大禁乎。此等义理昭然易见。而人鲜能知之。可胜叹哉。噫。他人之不化于 圣化者。吾无如之何。若夫与我相从讲学之士。而或有染于时俗。则是吾之深耻也。玆敢揭此诰之。以勖其不陷于不忠不孝之科也。
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朱夫子戒长子受之书曰。不惟饮酒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己忤人。尤当深戒。是知酒之可怕。无异于淫声美色。欲饬身修行者。自当远之。而至于今日我国之人。尤当疏绝之不暇。盖我 圣上以酒之为物。能使人丧性。又空费许多米谷。遂为永绝之计。三令五申。以告谕中外臣民。而犹恐其或不从。乃于太庙祭享。亦废用酒。代以醴齐。故我国士大夫。亦不敢用酒于家庙私祭。然愚民顽氓。狃于熟习。不忍私欲。潜酿盗饮。暗卖要利者。往往有之。至于刑辟而亦不止。其为难化。有甚于商之顽民。而士族亦不免此习。亲知相会。或有沽酒欢饮于稠人之中。而人之见之者。亦视以寻常。是何异于五季之时。居丧宴集。而腼然无愧。人亦恬不为怪者乎。孟子谓齐宣王曰。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入他国之礼。亦如是。而况居是邦。而不顾国之大禁乎。此等义理昭然易见。而人鲜能知之。可胜叹哉。噫。他人之不化于 圣化者。吾无如之何。若夫与我相从讲学之士。而或有染于时俗。则是吾之深耻也。玆敢揭此诰之。以勖其不陷于不忠不孝之科也。答或人
所询礼疑。顾此寡陋。何敢与议于此等变礼乎。然亦尝闻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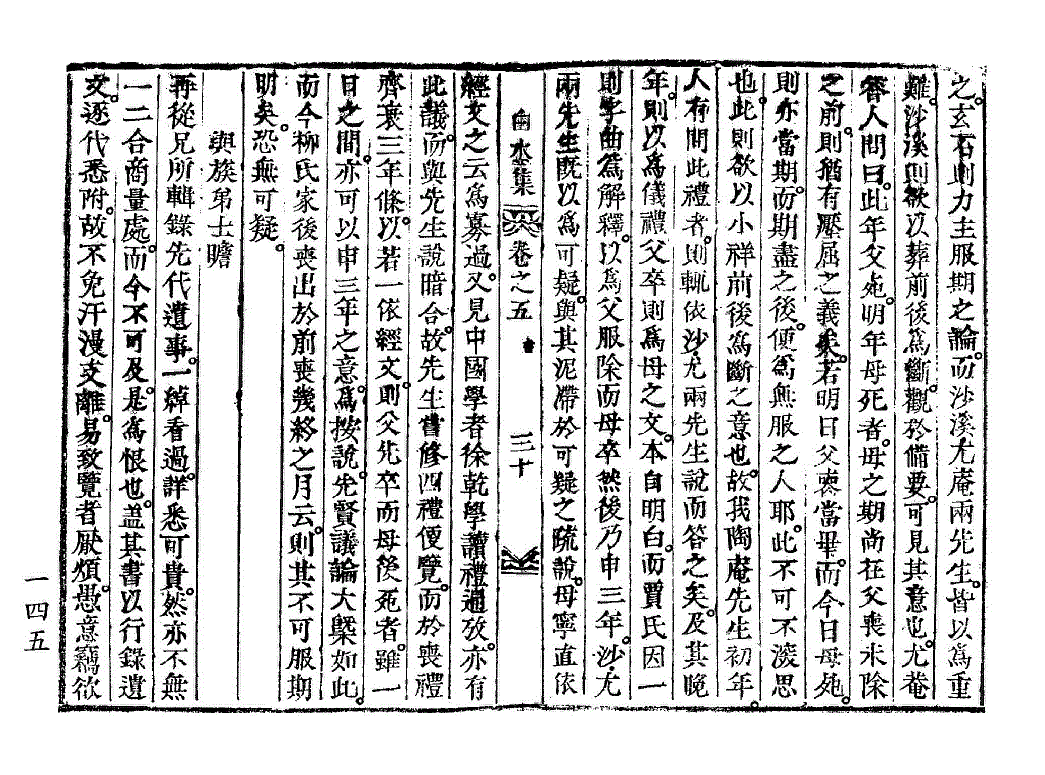 之。玄石则力主服期之论。而沙溪,尤庵两先生。皆以为重难。沙溪则欲以葬前后为断。观于备要。可见其意也。尤庵答人问曰。此年父死。明年母死者。母之期尚在父丧未除之前。则犹有压屈之义矣。若明日父丧当毕。而今日母死。则亦当期。而期尽之后。便为无服之人耶。此不可不深思也。此则欲以小祥前后为断之意也。故我陶庵先生初年。人有问此礼者。则辄依沙,尤两先生说而答之矣。及其晚年。则以为仪礼父卒则为母之文。本自明白。而贾氏因一则字曲为解释。以为父服除而母卒然后乃申三年。沙,尤两先生既以为可疑。与其泥滞于可疑之疏说。毋宁直依经文之云为寡过。又见中国学者徐乾学读礼通考。亦有此议。而与先生说暗合。故先生尝修四礼便览。而于丧礼齐衰三年条。以若一依经文。则父先卒而母后死者。虽一日之间。亦可以申三年之意。为按说。先贤议论大槩如此。而今柳氏家后丧出于前丧几终之月云。则其不可服期明矣。恐无可疑。
之。玄石则力主服期之论。而沙溪,尤庵两先生。皆以为重难。沙溪则欲以葬前后为断。观于备要。可见其意也。尤庵答人问曰。此年父死。明年母死者。母之期尚在父丧未除之前。则犹有压屈之义矣。若明日父丧当毕。而今日母死。则亦当期。而期尽之后。便为无服之人耶。此不可不深思也。此则欲以小祥前后为断之意也。故我陶庵先生初年。人有问此礼者。则辄依沙,尤两先生说而答之矣。及其晚年。则以为仪礼父卒则为母之文。本自明白。而贾氏因一则字曲为解释。以为父服除而母卒然后乃申三年。沙,尤两先生既以为可疑。与其泥滞于可疑之疏说。毋宁直依经文之云为寡过。又见中国学者徐乾学读礼通考。亦有此议。而与先生说暗合。故先生尝修四礼便览。而于丧礼齐衰三年条。以若一依经文。则父先卒而母后死者。虽一日之间。亦可以申三年之意。为按说。先贤议论大槩如此。而今柳氏家后丧出于前丧几终之月云。则其不可服期明矣。恐无可疑。与族弟士瞻
再从兄所辑录先代遗事。一绰看过。详悉可贵。然亦不无一二合商量处。而今不可及。是为恨也。盖其书以行录遗文。逐代悉附。故不免汗漫支离。易致览者厌烦。愚意窃欲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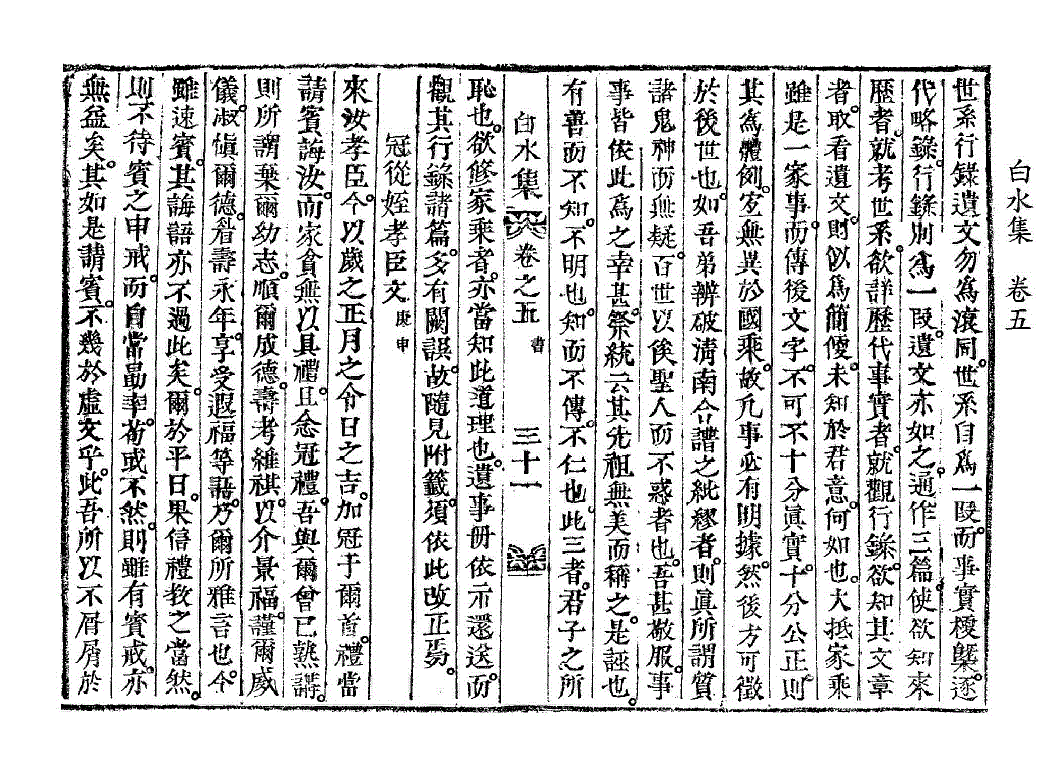 世系行录遗文勿为滚同。世系自为一段。而事实梗槩。逐代略录。行录别为一段。遗文亦如之。通作三篇。使欲知来历者。就考世系。欲详历代事实者。就观行录。欲知其文章者。取看遗文。则似为简便。未知于君意。何如也。大抵家乘虽是一家事。而传后文字。不可不十分真实。十分公正。则其为体例。宜无异于国乘。故凡事必有明据。然后方可徵于后世也。如吾弟辨破清南合谱之纰缪者。则真所谓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吾甚敬服。事事皆依此为之幸甚。祭统云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欲修家乘者。亦当知此道理也。遗事册依示还送。而观其行录诸篇。多有阙误。故随见附签。须依此改正焉。
世系行录遗文勿为滚同。世系自为一段。而事实梗槩。逐代略录。行录别为一段。遗文亦如之。通作三篇。使欲知来历者。就考世系。欲详历代事实者。就观行录。欲知其文章者。取看遗文。则似为简便。未知于君意。何如也。大抵家乘虽是一家事。而传后文字。不可不十分真实。十分公正。则其为体例。宜无异于国乘。故凡事必有明据。然后方可徵于后世也。如吾弟辨破清南合谱之纰缪者。则真所谓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吾甚敬服。事事皆依此为之幸甚。祭统云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欲修家乘者。亦当知此道理也。遗事册依示还送。而观其行录诸篇。多有阙误。故随见附签。须依此改正焉。冠从侄孝臣文(庚申)
来汝孝臣。今以岁之正月之令日之吉。加冠于尔首。礼当请宾诲汝。而家贫无以具礼。且念冠礼。吾与尔曾已熟讲。则所谓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以介景福。谨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永年。享受遐福等语。乃尔所雅言也。今虽速宾。其诲语亦不过此矣。尔于平日。果信礼教之当然。则不待宾之申戒。而自当勖率。苟或不然。则虽有宾戒。亦无益矣。其如是请宾。不几于虚文乎。此吾所以不屑屑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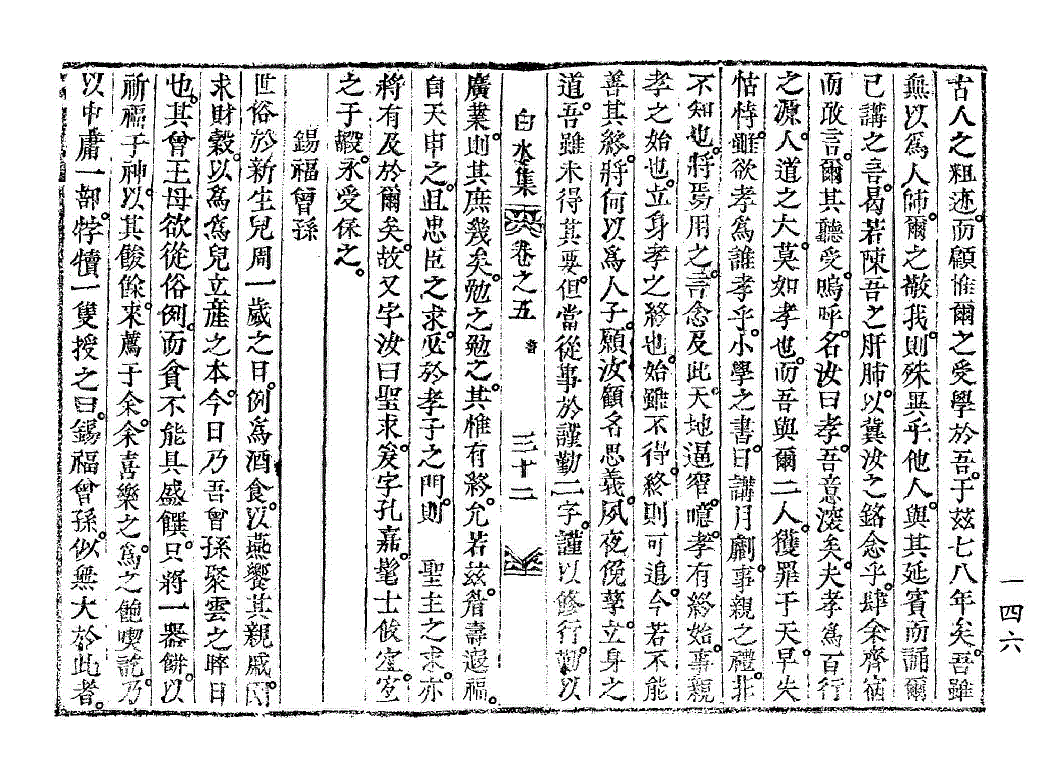 古人之粗迹。而顾惟尔之受学于吾。于玆七八年矣。吾虽无以为人师。尔之敬我。则殊异乎他人。与其延宾而诵尔已讲之言。曷若陈吾之肝肺。以冀汝之铭念乎。肆余齐宿而敢言。尔其听受。呜呼。名汝曰孝。吾意深矣。夫孝为百行之源。人道之大。莫如孝也。而吾与尔二人。获罪于天。早失怙恃。虽欲孝为谁孝乎。小学之书。日讲月劘。事亲之礼。非不知也。将焉用之。言念及此。天地逼窄。噫。孝有终始。事亲孝之始也。立身孝之终也。始虽不得。终则可追。今若不能善其终。将何以为人子。愿汝顾名思义。夙夜俛孳。立身之道。吾虽未得其要。但当从事于谨勤二字。谨以修行。勤以广业。则其庶几矣。勉之勉之。其惟有终。允若玆。眉寿遐福。自天申之。且忠臣之求。必于孝子之门。则 圣主之求。亦将有及于尔矣。故又字汝曰圣求。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古人之粗迹。而顾惟尔之受学于吾。于玆七八年矣。吾虽无以为人师。尔之敬我。则殊异乎他人。与其延宾而诵尔已讲之言。曷若陈吾之肝肺。以冀汝之铭念乎。肆余齐宿而敢言。尔其听受。呜呼。名汝曰孝。吾意深矣。夫孝为百行之源。人道之大。莫如孝也。而吾与尔二人。获罪于天。早失怙恃。虽欲孝为谁孝乎。小学之书。日讲月劘。事亲之礼。非不知也。将焉用之。言念及此。天地逼窄。噫。孝有终始。事亲孝之始也。立身孝之终也。始虽不得。终则可追。今若不能善其终。将何以为人子。愿汝顾名思义。夙夜俛孳。立身之道。吾虽未得其要。但当从事于谨勤二字。谨以修行。勤以广业。则其庶几矣。勉之勉之。其惟有终。允若玆。眉寿遐福。自天申之。且忠臣之求。必于孝子之门。则 圣主之求。亦将有及于尔矣。故又字汝曰圣求。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锡福曾孙
世俗于新生儿周一岁之日。例为酒食。以燕飨其亲戚。因求财谷。以为为儿立产之本。今日乃吾曾孙聚云之晬日也。其曾王母欲从俗例。而贫不能具盛馔。只将一器饼。以祈福于神。以其馂馀。来荐于余。余喜乐之。为之饱吃讫。乃以中庸一部。牸犊一只授之曰。锡福曾孙。似无大于此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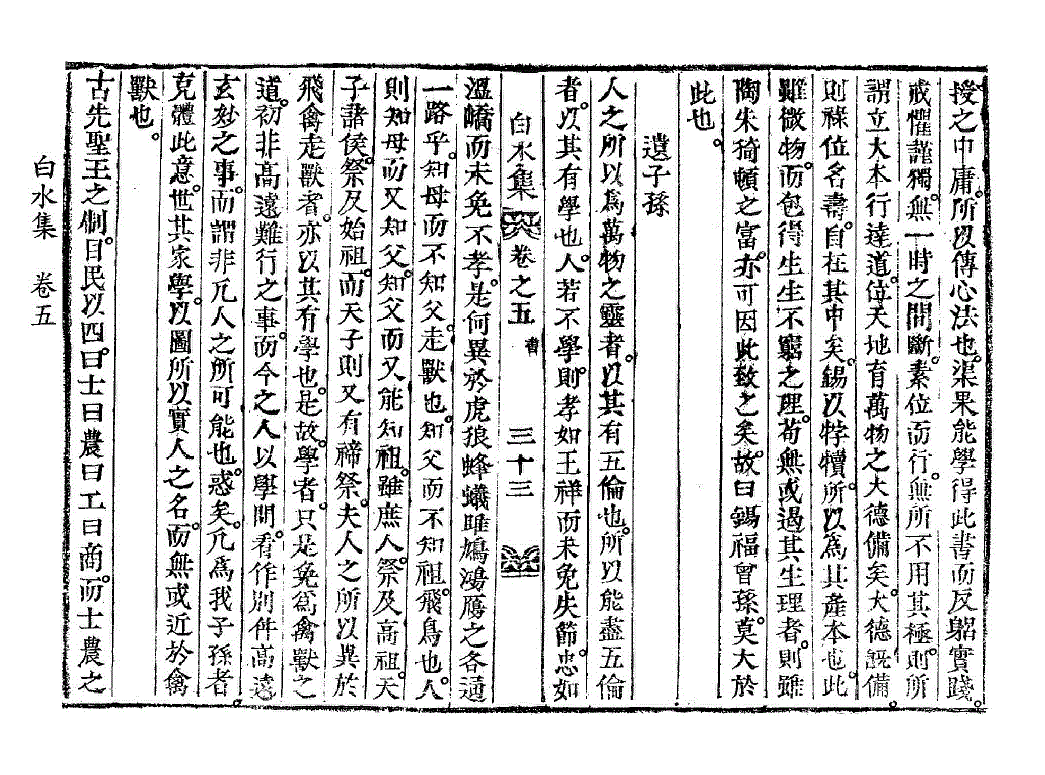 授之中庸。所以传心法也。渠果能学得此书而反躬实践。戒惧谨独。无一时之间断。素位而行。无所不用其极。则所谓立大本行达道。位天地育万物之大德备矣。大德既备。则禄位名寿。自在其中矣。锡以牸犊。所以为其产本也。此虽微物。而包得生生不穷之理。苟无或遏其生理者。则虽陶朱猗顿之富。亦可因此致之矣。故曰锡福曾孙。莫大于此也。
授之中庸。所以传心法也。渠果能学得此书而反躬实践。戒惧谨独。无一时之间断。素位而行。无所不用其极。则所谓立大本行达道。位天地育万物之大德备矣。大德既备。则禄位名寿。自在其中矣。锡以牸犊。所以为其产本也。此虽微物。而包得生生不穷之理。苟无或遏其生理者。则虽陶朱猗顿之富。亦可因此致之矣。故曰锡福曾孙。莫大于此也。遗子孙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以其有五伦也。所以能尽五伦者。以其有学也。人若不学。则孝如王祥而未免失节。忠如温峤而未免不孝。是何异于虎狼蜂蚁雎鸠鸿雁之各通一路乎。知母而不知父。走兽也。知父而不知祖。飞鸟也。人则知母而又知父。知父而又能知祖。虽庶人。祭及高祖。天子诸侯。祭及始祖。而天子则又有禘祭。夫人之所以异于飞禽走兽者。亦以其有学也。是故。学者。只是免为禽兽之道。初非高远难行之事。而今之人以学问。看作别件高远玄妙之事。而谓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惑矣。凡为我子孙者。克体此意。世其家学。以图所以实人之名。而无或近于禽兽也。
古先圣王之制。目民以四。曰士曰农曰工曰商。而士农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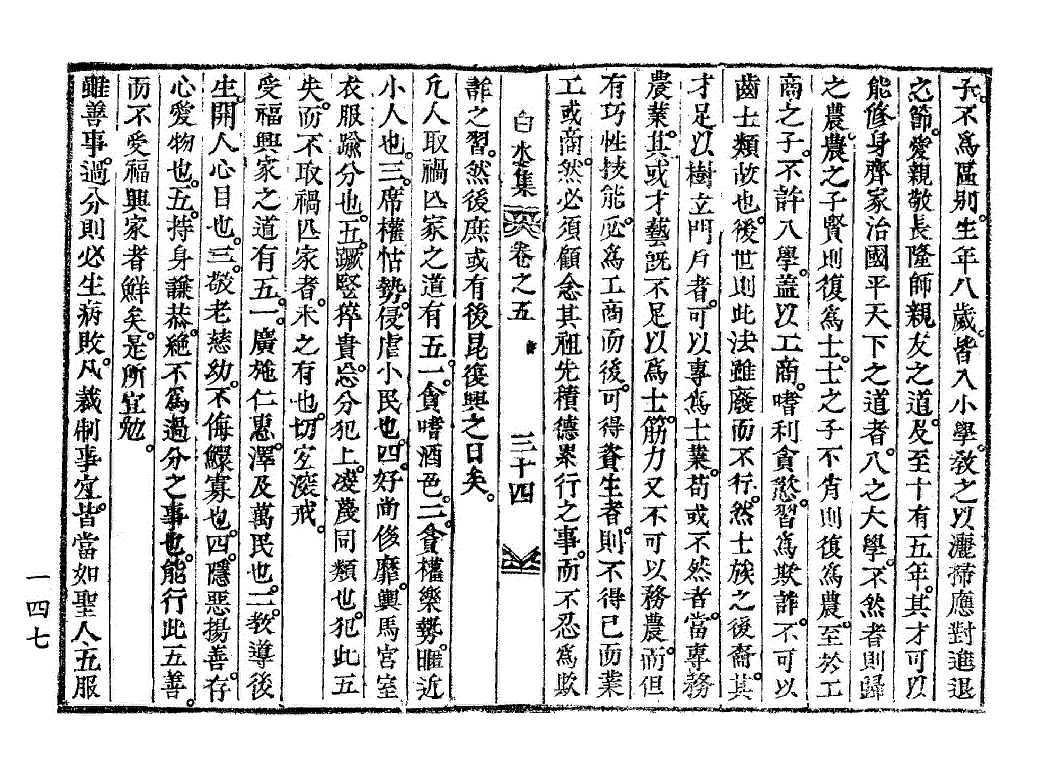 子。不为区别。生年八岁。皆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及至十有五年。其才可以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入之大学。不然者则归之农。农之子贤则复为士。士之子不肖则复为农。至于工商之子。不许入学。盖以工商。嗜利贪欲。习为欺诈。不可以齿士类故也。后世则此法虽废而不行。然士族之后裔。其才足以树立门户者。可以专为士业。苟或不然者。当专务农业。其或才艺既不足以为士。筋力又不可以务农。而但有巧性技能。必为工商而后。可得资生者。则不得已而业工或商。然必须顾念其祖先积德累行之事。而不忍为欺诈之习。然后庶或有后昆复兴之日矣。
子。不为区别。生年八岁。皆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及至十有五年。其才可以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者。入之大学。不然者则归之农。农之子贤则复为士。士之子不肖则复为农。至于工商之子。不许入学。盖以工商。嗜利贪欲。习为欺诈。不可以齿士类故也。后世则此法虽废而不行。然士族之后裔。其才足以树立门户者。可以专为士业。苟或不然者。当专务农业。其或才艺既不足以为士。筋力又不可以务农。而但有巧性技能。必为工商而后。可得资生者。则不得已而业工或商。然必须顾念其祖先积德累行之事。而不忍为欺诈之习。然后庶或有后昆复兴之日矣。凡人取祸亡家之道有五。一。贪嗜酒色。二。贪权乐势。昵近小人也。三。席权怙势。侵虐小民也。四。好尚侈靡。舆马宫室衣服踰分也。五。蹶竖猝贵。忘分犯上。凌蔑同类也。犯此五失。而不取祸亡家者。未之有也。切宜深戒。
受福兴家之道有五。一。广施仁惠。泽及万民也。二。教导后生。开人心目也。三。敬老慈幼。不侮鳏寡也。四。隐恶扬善。存心爱物也。五。持身谦恭。绝不为过分之事也。能行此五善。而不受福兴家者鲜矣。是所宜勉。
虽善事。过分则必生病败。凡裁制事宜。皆当如圣人五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第 14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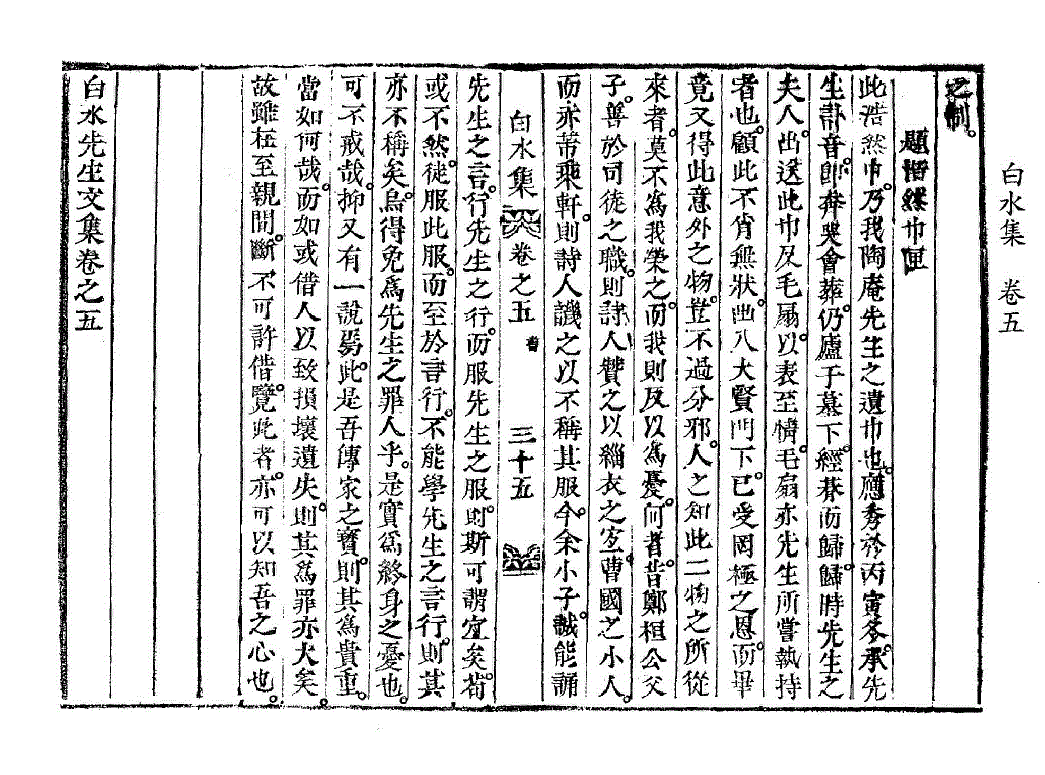 之制。
之制。题浩然巾匣
此浩然巾。乃我陶庵先生之遗巾也。应秀于丙寅冬。承先生讣音。即奔哭会葬。仍庐于墓下。经期而归。归时先生之夫人。出送此巾及毛扇。以表至情。毛扇亦先生所尝执持者也。顾此不肖无状。出入大贤门下。已受罔极之恩。而毕竟又得此意外之物。岂不过分邪。人之知此二物之所从来者。莫不为我荣之。而我则及以为忧。何者。昔郑桓公父子。善于司徒之职。则诗人赞之以缁衣之宜。曹国之小人。而赤芾乘轩。则诗人讥之以不称其服。今余小子。诚能诵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而服先生之服。则斯可谓宜矣。苟或不然。徒服此服。而至于言行。不能学先生之言行。则其亦不称矣。乌得免为先生之罪人乎。是实为终身之忧也。可不戒哉。抑又有一说焉。此是吾传家之宝。则其为贵重。当如何哉。而如或借人以致损坏遗失。则其为罪亦大矣。故虽在至亲间。断不可许借。览此者。亦可以知吾之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