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书
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4H 页
 答梁恭伯(学谦)
答梁恭伯(学谦)明德。专以本心为喻者。有见于朱子书耶。
朱子书中。未见其有曰明德是本心者。然朱子论心处。每每言虚言灵。或言虚灵。或言虚明。或言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此与明德章句所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有何不同乎。此玉溪卢氏所以以明德谓之本心。而吾师之所以从其说也。
追考语类云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朱子既以良心为明德。则良心非本心乎。此足为专以本心为明德之證。而当时未及考见。故不能引證。固陋可愧。)
来谕引语类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明一条。以为明德不可谓本心之證。以愚观之。恐高明不识语类本意也。按语类明德说有三条。而有曰。天之赋于人物者谓之命。人与物受之者谓之性。主于一身者谓之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以此一条观之则有若以明德不属于心性而别为一物者然。朱子本意则不然。此则当活看也。又有问明德。合是性合是心。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以此一条观之。则分明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4L 页
 明德为兼心性合体用而言之也。又有问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明。此一条。亦兼心性而言也。盖仁义礼智者理也。心者合理气之名。而若对性而言。则心为气也。理不能光明照彻。而必得心气然后。乃能光明照彻。而无一毫之不明。此之谓明德。故朱子既不专属性。又不专属心。而必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此乃合理气兼体用而言也。合理气而兼体用者。谓之心则可也。谓之性则不可。然心之为名。有精底有粗底。苟但曰明德是心。则无以见其明德之为纯粹至善也。故玉溪以为本心。此其下语。极为精密。今高明偶失照勘于朱子之训。以光明照彻专属理。而不兼心气看。故必以明德谓之性。而力排本心之说。是诚有得于朱子性却实之意。其如有违于心之意亦多之训何。愿以此更商也。
明德为兼心性合体用而言之也。又有问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言。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无一毫不明。此一条。亦兼心性而言也。盖仁义礼智者理也。心者合理气之名。而若对性而言。则心为气也。理不能光明照彻。而必得心气然后。乃能光明照彻。而无一毫之不明。此之谓明德。故朱子既不专属性。又不专属心。而必曰这个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此乃合理气兼体用而言也。合理气而兼体用者。谓之心则可也。谓之性则不可。然心之为名。有精底有粗底。苟但曰明德是心。则无以见其明德之为纯粹至善也。故玉溪以为本心。此其下语。极为精密。今高明偶失照勘于朱子之训。以光明照彻专属理。而不兼心气看。故必以明德谓之性。而力排本心之说。是诚有得于朱子性却实之意。其如有违于心之意亦多之训何。愿以此更商也。或问曰。此德之明。日益昏昧。此心之灵。其所知者。情欲利害之私而已。以德与心每每对言。则以明德专以本心为谕者。其果恰当乎。
愚按或问所谓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者。谓道心之愈微也。此心之灵。其所知者。情欲利害之私而已者。谓人心之愈危也。人心道心。迭为胜负者。岂不可对举说也。而道心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5H 页
 是本心也。于此亦可见朱子之以明德贴心之意也。高明何疑焉。
是本心也。于此亦可见朱子之以明德贴心之意也。高明何疑焉。论语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以仁不谓之本心。而必曰本心之全德。则心与德。必有分间。
集注说。泛然观之。则心与德似有分间。然朱子本意。则初非分别言之也。故朱子于仁说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为心。感兴诗曰。恭惟皇上帝。降此仁义心。此非直以仁义为本心者乎。
明儒黄际飞之言曰。大学言心不言性。此语最是鹘突。何尝不言性。即仁义礼智之性。载在心里。所谓明德者。何尝单言心。有这道理在心里。乃光明照彻。乃为明德。又曰。心非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玉溪所谓明德。只是本心。最是乱道云云。此说有合于朱子。则岂不取乎。
以愚观之。黄际飞所谓明德者。何尝单言心。有道理在心里。乃光明照彻。乃为明德者。无所违于朱子之言。此则可谓依样画葫芦而不失者也。然不知本心之为此光明照彻者。而反斥玉溪以乱道。则其无实见得。据此可知。而其认本心以粗底心。而属明德于理一边者。与高明所见。若合符节。宜高明之喜乐而援引也。若谓之有合于朱子。则恐不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5L 页
 小学题辞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然则明德即在心之理。而有体有用。亦无有内外之间者也。言其体则即浑然之性也。言其用则即灿然之道也。
小学题辞曰。明命赫然。罔有内外。然则明德即在心之理。而有体有用。亦无有内外之间者也。言其体则即浑然之性也。言其用则即灿然之道也。愚按小学题辞。以一性字终始之。则所谓明命赫然者。亦指性而言。故释之者曰。明命即天之所赋于人而人之所得以为性者。此与明德章句所谓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意有不同。高明乃引彼證此。愚未知其信然也。且明德之体用。章句具众理应万事二句。已备言之矣。高明乃别为注脚。以为其体则浑然之性也。其用则灿然之道也。是则恐难免杜撰之讥也。
若如高明之见。而以属于心而言之。则必有心与理之无别也。若如愚说而以属于性而言之。则恐或有举其体而遗其用也。然以明德专属于本心。则决然不是。但以明德为性。则虽有举体遗用之病。明德与性。具是在心之理。则舍性而求明德于性外者。未知其为可。
朱子语类及大学章句所释明德之说。莫不合理气兼体用而言。未尝有举体遗用之说。而愚所谓本心者。即是合理气兼体用之谓也。高明乃曰。以明德专属于本心。则决然不是。必以高明举体遗用之说为是而专属性何也。高明又力攻鄙人意虽极其诚而亦不可无正心工夫之说。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6H 页
 广譬曲谕。既勤且劳。其眷厚之意。则诚为可感。然此非鄙说。乃朱子之说。则舍己从人之道。恐不可行于此等处也。奈何奈何。按语类康叔问意既诚矣。心安有不正。朱子曰。诚只是实。虽是意诚。然心之所发。有不中节处。依旧未是正。又曰。不成说我意已诚矣。心将自正。则恐惧好恶忿𢜀引将去。又却邪了。须是无所不用其极。又曰。意未诚则全体是私意矣。理会甚正心。然意虽诚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又曰。要紧最是诚意时节。若打得这关过。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又曰。大学所以有许多节次。正欲教人逐节用功。非如一无节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到平天下也。人盖有意诚而心未正者。故于忿𢜀等。诚不可不随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不修者。故于好恶閒。诚不可不随人而节制。齐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功。故经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诚意而来。修身者必自正心而来。非谓意既诚则心无事乎正。心既正则身无事乎修也。观此数条。则可知愚言之不为无据也。何高明攻斥之不已也。高明每以诚意之诚。为非十分诚。今此朱子十分清了一句。不足为破惑之明證乎。
广譬曲谕。既勤且劳。其眷厚之意。则诚为可感。然此非鄙说。乃朱子之说。则舍己从人之道。恐不可行于此等处也。奈何奈何。按语类康叔问意既诚矣。心安有不正。朱子曰。诚只是实。虽是意诚。然心之所发。有不中节处。依旧未是正。又曰。不成说我意已诚矣。心将自正。则恐惧好恶忿𢜀引将去。又却邪了。须是无所不用其极。又曰。意未诚则全体是私意矣。理会甚正心。然意虽诚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又曰。要紧最是诚意时节。若打得这关过。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于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时节。已是淘去了浊十分清了。又怕于清里面。有波浪动荡处。又曰。大学所以有许多节次。正欲教人逐节用功。非如一无节之竹。使人才能格物。便到平天下也。人盖有意诚而心未正者。故于忿𢜀等。诚不可不随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不修者。故于好恶閒。诚不可不随人而节制。齐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功。故经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诚意而来。修身者必自正心而来。非谓意既诚则心无事乎正。心既正则身无事乎修也。观此数条。则可知愚言之不为无据也。何高明攻斥之不已也。高明每以诚意之诚。为非十分诚。今此朱子十分清了一句。不足为破惑之明證乎。高明又引晦庵栗谷两先生之说。以斥鄙所谓颜子意极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6L 页
 其诚之说。此亦未免苟且矣。盖朱子所引三月不违之言。乃极论实心间断之理。而取喻偶及于此也。非谓颜子犹未至意诚之域也。此所谓过去说。不可以实看也。栗谷之言。则似可为援据。然质之以朱子之言。则有所不合。何者。朱子之言曰。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尝复行。便是意之实。又曰。如颜子不迁怒。可怒在物。颜子未尝有血气所动而移于人也。此两条语。已为颜子知至意诚心正之明證也。且朱子尝云颜子优于汤武。如汤武反之之圣。不可谓之知未至意未诚心未正。况优于汤武者乎。此栗翁之说。所以不合于朱子之训也。虽欲从之。有不可得矣。盖三月不违者。非谓三月之后因以违仁也。只是霎然之境。微有差失。而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则意何尝不极其诚。心何尝不极其正乎。如是推之。则非但高明所谓意未十分诚者为不是。鄙之前所云心未十分正者亦非也。然君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则如心意之别。诚正之分。讲而明之。以为体行之地。固为说约之道也。至于意诚心正之功效。颜子诚意之尽否。则力辨何为。此所谓无益之辨。不急之察。姑为舍置如何。
其诚之说。此亦未免苟且矣。盖朱子所引三月不违之言。乃极论实心间断之理。而取喻偶及于此也。非谓颜子犹未至意诚之域也。此所谓过去说。不可以实看也。栗谷之言。则似可为援据。然质之以朱子之言。则有所不合。何者。朱子之言曰。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尝复行。便是意之实。又曰。如颜子不迁怒。可怒在物。颜子未尝有血气所动而移于人也。此两条语。已为颜子知至意诚心正之明證也。且朱子尝云颜子优于汤武。如汤武反之之圣。不可谓之知未至意未诚心未正。况优于汤武者乎。此栗翁之说。所以不合于朱子之训也。虽欲从之。有不可得矣。盖三月不违者。非谓三月之后因以违仁也。只是霎然之境。微有差失。而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则意何尝不极其诚。心何尝不极其正乎。如是推之。则非但高明所谓意未十分诚者为不是。鄙之前所云心未十分正者亦非也。然君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则如心意之别。诚正之分。讲而明之。以为体行之地。固为说约之道也。至于意诚心正之功效。颜子诚意之尽否。则力辨何为。此所谓无益之辨。不急之察。姑为舍置如何。正心章不得其正。高明则以为心之体用。俱不得其正。愚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7H 页
 则以为心之用。不得其正。心之体则未尝不正。累日辨难。费了多少说话。而不得归一。高明今复有此缕缕。而别无前日所未闻之言。则何以解此愚迷之惑也。盖正心之心字。语类以为包体用而言。此与高明所谓合体用而言者。似同而实异。朱子则只言是心包体用而言。高明则谓不得其正。合体用而言。此其语意绝不相同也。且语类云虽是意诚。心之所发。有不中节处。依旧未是正。又曰。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无。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应物之时。不可夹带私心。如有一项事可喜。自家正喜。蓦见一可怒底事来。是当怒之事。却以这喜心处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又曰。忿𢜀事过。便当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懥留在这里。如何得心正。此三条者。非皆指用处说者乎。盖体用非是二物。心则一也。动则为用。静则为体。动者。已发之谓也。静者。未发之谓也。未发则中也。中何尝有不正乎。惟发然后有正不正之分。发而中节则是得其正。不中节则是不得其正。故朱子论心字。则曰包体用而言。又曰。心又是该动静。论正心工夫。则曰正心但存得此心在这里。所谓忿𢜀恐惧好乐忧患自来不得。此则言存养于静时也。又曰。于忿懥等。诚不可不随事而排遣。此则言省察于动时也。是则正心工夫。亦通动静言之也。至于言
则以为心之用。不得其正。心之体则未尝不正。累日辨难。费了多少说话。而不得归一。高明今复有此缕缕。而别无前日所未闻之言。则何以解此愚迷之惑也。盖正心之心字。语类以为包体用而言。此与高明所谓合体用而言者。似同而实异。朱子则只言是心包体用而言。高明则谓不得其正。合体用而言。此其语意绝不相同也。且语类云虽是意诚。心之所发。有不中节处。依旧未是正。又曰。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无。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应物之时。不可夹带私心。如有一项事可喜。自家正喜。蓦见一可怒底事来。是当怒之事。却以这喜心处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又曰。忿𢜀事过。便当豁然。便得其正。若只管忿懥留在这里。如何得心正。此三条者。非皆指用处说者乎。盖体用非是二物。心则一也。动则为用。静则为体。动者。已发之谓也。静者。未发之谓也。未发则中也。中何尝有不正乎。惟发然后有正不正之分。发而中节则是得其正。不中节则是不得其正。故朱子论心字。则曰包体用而言。又曰。心又是该动静。论正心工夫。则曰正心但存得此心在这里。所谓忿𢜀恐惧好乐忧患自来不得。此则言存养于静时也。又曰。于忿懥等。诚不可不随事而排遣。此则言省察于动时也。是则正心工夫。亦通动静言之也。至于言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7L 页
 心之不得其正。则语类诸说。皆指用处而言。章句及或问。又皆曰其用之所行。不得其正。未尝有心体不得其正之训。而高明则力主心体不正之论何故。高明每好为畔背朱训之论也。噫。朱子孔子后孔子也。欲学圣人之道。而不师朱子则不得。愿更商量也。
心之不得其正。则语类诸说。皆指用处而言。章句及或问。又皆曰其用之所行。不得其正。未尝有心体不得其正之训。而高明则力主心体不正之论何故。高明每好为畔背朱训之论也。噫。朱子孔子后孔子也。欲学圣人之道。而不师朱子则不得。愿更商量也。答梁恭伯
受赐于长者之礼。朱子曰古者。赐之车则乘而拜。赐之衣服则服而拜。赐之饮食则尝而拜之。礼记玉藻云大夫亲赐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不服而拜。敌者不在拜于其室。由此观之。则上自君大夫。下至敌者之赐。莫不有拜受之礼。何独于长者之赐。无拜受之节也。然古礼。今不尽行。长者。亦有多少般所赐之物。又有轻重之别。则恐难一一尽拜。此则惟在行礼者之随时酌处也。
长者有书问。拜受与否。未有所闻。昔游泉上时。见有一人拜受其父兄之书者。是必有所见而然。偶未之问焉。追恨追恨。古今书札。例用承拜字。是必有来历。岂古人见书。则有拜礼故邪。至于长者传语。则起身致敬者。世多有之。故愚亦从之。盖于此二者。皆有拜礼。似为曲尽。而习俗难可猝变。奈何。
答梁恭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8H 页
 高明引张子言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及语类知得有道理光明不昧云云二条。以为性亦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之證案。愚谓朱子之释明德也。既言虚。又言灵者。以虚字不足以兼灵字义也。既言虚灵。又言不昧者。以虚灵不足以兼不昧之义也。既言虚灵不昧。又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以但言虚灵不昧。不若兼言具众理应万事之为完备也。今高明所引之言。则既遗却灵字。又阙却具众理应万事。只以虚字与光明不昧字。欲括尽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之义。不亦疏乎。
高明引张子言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及语类知得有道理光明不昧云云二条。以为性亦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之證案。愚谓朱子之释明德也。既言虚。又言灵者。以虚字不足以兼灵字义也。既言虚灵。又言不昧者。以虚灵不足以兼不昧之义也。既言虚灵不昧。又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以但言虚灵不昧。不若兼言具众理应万事之为完备也。今高明所引之言。则既遗却灵字。又阙却具众理应万事。只以虚字与光明不昧字。欲括尽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之义。不亦疏乎。安有道理必得心气。然后乃能光明照彻云云。
愚谓光明照彻四字。与只言一明字者。义有不同。故朱子之论天理。未尝言光明照彻。而只言明命。及论明德。然后方言这道理在心里。光明照彻。其意可知也。高明不察此意。明命之明字。亦兼照彻意看。而谓道理自能光明照彻。则愚之见斥。势所不免也。愚尝闻朱子之言曰。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燄。以此推之。则愚之所谓理不能光明照彻。而必得心气。然后乃能光明照彻者。不为无据之说也。此是道理之至微至妙处。愿更商量。
栗谷曰。合心性而总名曰明德。则犹张子所谓合虚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8L 页
 气。有性之名之意也。如是立言。可以完备无弊矣。
气。有性之名之意也。如是立言。可以完备无弊矣。此则来谕极是极是。但未知高明既以此栗翁之说。为完备无弊。则愚之所谓本心者。乃指合性与气而言者也。而高明反斥之。而固守自家专言理之说何也。
语类曰。舍心无以见性。舍性无以见心。故孟子言性。每每相随说。如仁义礼智是性。然又有说仁义之心。这是性与心通说。恻隐羞恶是情。又说恻隐羞恶之心。这是情与心通说。这是性情皆主于心。故恁地通说。
性情皆主于心。故孟子于性与心说。既恁地通说。而朱子亦以性与心恁地通说。则此语类说。固可为通说心性者之證案。高明乃引之。以为分别德与心之證。吾未见其衬著也。
朱子答陈器之书曰。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其下又曰。仁之理便应。礼之理便应。以此观之。具与应。何关于心乎。
噫。高明果以此所谓含具万理者。谓同于心之具众理乎。愚以为此所谓含具万理者。谓一性字包得万理也。此犹言仁包四端也。心之具众理者。是神明之气包含该载性理也。具字虽同。而义则各异。高明比而同之。如之何其可也。高明又果以仁之理便应。礼之理便应。谓真无异于心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9H 页
 之应万事乎。愚以为能感应者心也。所以感应者理也。而恻隐之感发。由于仁之理。恭敬之感发。由于礼之理。故朱子言其浑然之中。各有条理。而有此仁之理便应。礼之理便应之说。非谓性之自能感应。如心之感应也。故仁之理便应之下。必言恻隐之心于是乎形。礼之理便应之下。亦言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观此可见朱子之以能感应者为心。而所以感应者为性之意也。高明乃以此而谓具与应。何关于心乎。若如高明之言。则虽无此心。性能具众理而应万事乎。朱子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今以高明之言。则是动处为性也。其可乎。虽只业词章者。必不为之也。熟谓高明而有此乎。且高明于具与应。何关于心之下。又引玉溪说吾心之体。即明德之虚而具众理者。吾心之用。即明德之灵而应万事者。以为明德非混于心之證。此亦何所见也。以愚观之。玉溪说既曰。吾心之体。即明德之虚而具众理者。则是具众理之关于心。而可见明德之无别于心也。又曰。吾心之用。即明德之灵而应万事者。则是应万事之关于心。而又可见明德之无别于心也。盖玉溪此等说。皆所以发明明德之为本心。故云然也。高明每引之以为专言性之證。愚昧实不知其故也。
之应万事乎。愚以为能感应者心也。所以感应者理也。而恻隐之感发。由于仁之理。恭敬之感发。由于礼之理。故朱子言其浑然之中。各有条理。而有此仁之理便应。礼之理便应之说。非谓性之自能感应。如心之感应也。故仁之理便应之下。必言恻隐之心于是乎形。礼之理便应之下。亦言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观此可见朱子之以能感应者为心。而所以感应者为性之意也。高明乃以此而谓具与应。何关于心乎。若如高明之言。则虽无此心。性能具众理而应万事乎。朱子曰。动处是心。动底是性。今以高明之言。则是动处为性也。其可乎。虽只业词章者。必不为之也。熟谓高明而有此乎。且高明于具与应。何关于心之下。又引玉溪说吾心之体。即明德之虚而具众理者。吾心之用。即明德之灵而应万事者。以为明德非混于心之證。此亦何所见也。以愚观之。玉溪说既曰。吾心之体。即明德之虚而具众理者。则是具众理之关于心。而可见明德之无别于心也。又曰。吾心之用。即明德之灵而应万事者。则是应万事之关于心。而又可见明德之无别于心也。盖玉溪此等说。皆所以发明明德之为本心。故云然也。高明每引之以为专言性之證。愚昧实不知其故也。高明引胡云峰说小德川流。是其灿然者。大德敦化。是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89L 页
 浑然者云云。愚之以高明所释明德体用之说。谓难免杜撰之讥者。非谓浑然灿然之说。为无稽也。盖性与明德。义有不同。故朱子于中庸章句释天命之性。则曰性即理也。于大学章句释明德。则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盖性则与道为体用。而为专言理者也。明德则以具众理应万事为体用。而为兼言理气者也。故不可以释性之言释明德。又不可以释明德之说释性也。高明则不遵朱子之章句。而自以其体则浑然之性。其用则灿然之道等句语。别立注释。此正杜撰注所谓杜前人说话。撰出新语者也。
浑然者云云。愚之以高明所释明德体用之说。谓难免杜撰之讥者。非谓浑然灿然之说。为无稽也。盖性与明德。义有不同。故朱子于中庸章句释天命之性。则曰性即理也。于大学章句释明德。则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盖性则与道为体用。而为专言理者也。明德则以具众理应万事为体用。而为兼言理气者也。故不可以释性之言释明德。又不可以释明德之说释性也。高明则不遵朱子之章句。而自以其体则浑然之性。其用则灿然之道等句语。别立注释。此正杜撰注所谓杜前人说话。撰出新语者也。中庸。直以无声无臭赞德之妙。则德之专以理言之。可见矣。
愚闻朱子论中庸卒章之言曰。此章凡八引诗。自衣锦尚絅。以至不显维德凡五条。始学成德疏密浅深之序也。自不大声色。以至无声无臭凡三条。皆所以赞夫不显之德也。由此观之。此章所赞之德。乃是不显之德。所谓不显之德。即是充其尚絅之心。而谨独诚身。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德也。而高明绰见无声无臭之赞。遂谓是德为专言理者。何其迂阔也。
朱子曰。那藏相似云云。其所谓函非心之譬欤。里面点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0H 页
 灯。则非理之譬欤。然则光明灿烂。函之为乎。灯之为乎。以此取譬。则可见明德在心里。自能光明灿烂也。
灯。则非理之譬欤。然则光明灿烂。函之为乎。灯之为乎。以此取譬。则可见明德在心里。自能光明灿烂也。愚谓函非心之譬也。藏乃心之譬也。里面点灯。谓藏之里面点灯也。四方八面。皆如是光明灿烂。谓藏与灯合。而四方八面。皆如是光明灿烂也。如是看得。乃为心与理一之譬。若以函为心之譬。而曰除了经函。里面点灯云。则里面二字。无所著落。而不得为心与理一之譬也。如何如何。恰似之似。非误也。高明疑其与相似字重叠。故云然。然恰似之似。与相似之似。意有不同。恰似犹俗言마티也。故语类此等文法甚多。
来教曰。其以明德。不曰心不曰性。而必曰所得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者。以其仁义礼智之性。在人而光明正大。不混乎物之性故也。愚于此。特起疑端。何者。高明以道理谓本自光明照彻。故广引朱子许多论明命之说。以攻斥愚理得心气然后乃能光明照彻之言。则是固以在天之理。为本自光明照彻也。人与物匀禀此光明照彻之理。则是万物所禀之理。亦可谓之明德。而高明反谓光明正大不混于物之性者何也。岂天有光明之理。又有黑暗之理。而于人则赋以光明之理。于物则赋以黑暗之理欤。高明又有性是人与物所同得之理也。以本然言之。人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0L 页
 物初无所异之教。以此观之。则光明照彻之理。物亦得之。而谓物无明德者。何也。所引真西山之说。果为高明之證案。然西山之论心性。自多与朱子说相反处。此亦其一也。愚则不取也。莫如置而不论之教。诚为至当。盖吾辈以新学小生。不从事于小学。而遽论心性渊微之理者。实为躐等之事。则宜乎傍人之指笑也。何敢愠人之不知也。其在自家道理。止之为是。继自今实践斯言。幸甚幸甚。
物初无所异之教。以此观之。则光明照彻之理。物亦得之。而谓物无明德者。何也。所引真西山之说。果为高明之證案。然西山之论心性。自多与朱子说相反处。此亦其一也。愚则不取也。莫如置而不论之教。诚为至当。盖吾辈以新学小生。不从事于小学。而遽论心性渊微之理者。实为躐等之事。则宜乎傍人之指笑也。何敢愠人之不知也。其在自家道理。止之为是。继自今实践斯言。幸甚幸甚。答梁恭伯
正心章心不得其正之说。盛教缕缕多端。其中或问小注疏一段。乃其骨子也。盖此说极有条理。若使不知者而见之。则必以为不易之论也。然朱子本意。特明其有所之为病而已。初非谓是心之体亦不得其正也。而高明以己意。若是扭捏主张。极为未安。谨以愚见逐条劄疑于贵疏下。以备崇览。
贵疏曰。人心如一个镜。(体用之正。)先未有一个影象。(体之正。)有物事来。方始照见妍丑。(用之正。)
以上恐是。
若先有个影子在里面。(体不得其正。)
愚谓物未来之前。宁有镜中先有影象之理乎。惟应物之际。先有一物照入镜中。其影象犹在。而他物又来。则有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1H 页
 可照得。故朱子又曰。如镜有人影在里。而第二人来。便照不得。此非就用处言者乎。若物已去后。镜藏在奁中。而先有个影象。则谓之体不得其正可也。物未去之前。其影象之在镜里者。谓之体不正。则恐不可也。
可照得。故朱子又曰。如镜有人影在里。而第二人来。便照不得。此非就用处言者乎。若物已去后。镜藏在奁中。而先有个影象。则谓之体不得其正可也。物未去之前。其影象之在镜里者。谓之体不正。则恐不可也。如何照得。(用不得其正。)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体之正。)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照得高下轻重。(用之正。)
以上亦恐无病。
若事未来。先有一个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心在这里。(体不得其正。)
愚意此疏大不是。何者。朱子曰。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朱子语止此。)事未来。有一个忿𢜀好乐恐惧忧患之心者。是为未发欤。已发欤。若是未发境界。则谓之体不得其正可也。既有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心。则此是已发境界也。谓之体不得其正可乎。愚意此疏当曰有所之病也。
及忿𢜀好乐恐惧忧患之事到来。又以这心相与滚合。便失其正。(用不得其正。)
此则无病。
事了。又只若留在这里。如何得正。(体不得其正。)
愚意此疏亦不是。所谓事了留在者。非指忿懥好乐恐惧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1L 页
 忧患之情而言耶。事已去而情犹留在者。是乃发不中节者。则当谓之用不得其正。不当谓之体不得其正也。○大抵事未来而先有忿𢜀好乐恐惧忧患之心。事去后又只留在这里者。皆是有所之病也。既曰有所。则便是心之已动也。而高明以此谓之体不得其正。则其果合于朱子未发是体已发乃用之训乎。愿更商量也。
忧患之情而言耶。事已去而情犹留在者。是乃发不中节者。则当谓之用不得其正。不当谓之体不得其正也。○大抵事未来而先有忿𢜀好乐恐惧忧患之心。事去后又只留在这里者。皆是有所之病也。既曰有所。则便是心之已动也。而高明以此谓之体不得其正。则其果合于朱子未发是体已发乃用之训乎。愿更商量也。答梁恭伯
高明引大学或问小注说。以为明德不独在人。而物亦有之之證。此恐失朱子之本旨也。愚按或问之释明德条。曰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最为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由是观之。则明德之所以得名者。以其得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方寸之间。虚灵通彻。万理咸备故也。然则彼万物之有些明处者。何足谓之明德也。高明所引大全说。则只论人物之性。非论明德也。而若是并引者。良由高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2H 页
 以性与明德为一故也。然性与明德。有些分别。盖性则专是理。而明德兼理气而言者。故陈北溪释朱子虚灵洞澈万理咸备两句语曰。此八字。只是再详虚灵不昧以具众理之意。虚灵洞澈。盖理与气合而有此妙用耳。据此一说。可知明德之兼理气言也。夫理之在人在物。有全不全之异者。以人则有明德。而物则无明德也。故朱子之论明德说曰。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今高明则以理与明德混而一之。而谓禽兽亦有明德。其不悖于朱子之说乎。高明又以禽兽之有一点明处。为明德之一端。而谓物亦有此明德之一端。则明德之非心。于此可见。噫。物之所以有一点明处者。乃其心有一点明处故也。若以此为明德之一端。则于此尤可见明德之为心也。又何以见其明德之非心也耶。
以性与明德为一故也。然性与明德。有些分别。盖性则专是理。而明德兼理气而言者。故陈北溪释朱子虚灵洞澈万理咸备两句语曰。此八字。只是再详虚灵不昧以具众理之意。虚灵洞澈。盖理与气合而有此妙用耳。据此一说。可知明德之兼理气言也。夫理之在人在物。有全不全之异者。以人则有明德。而物则无明德也。故朱子之论明德说曰。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今高明则以理与明德混而一之。而谓禽兽亦有明德。其不悖于朱子之说乎。高明又以禽兽之有一点明处。为明德之一端。而谓物亦有此明德之一端。则明德之非心。于此可见。噫。物之所以有一点明处者。乃其心有一点明处故也。若以此为明德之一端。则于此尤可见明德之为心也。又何以见其明德之非心也耶。明德与四德。以其纯粹至善。不以气质之美恶。有所加损者而言之则一也。然其所指地头。则自有不同。明德是指心之本体虚灵不昧。以具众理应万事者而言。四德则是指心中所具之理。真实无妄者而言也。故朱子释仁字。则曰心之德爱之理。又曰。恻怛慈爱底理。其释义字。则曰断制裁割底理。礼则曰恭敬撙节底理。智则曰分别是非底理。此非专以理言者乎。其释明德。则曰是我得之于天。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2L 页
 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统而言之。则仁义礼智。以其发见而言之。如恻隐羞恶之类。以其实用言之。如事亲从兄。是也。此非以心统性情行事而言者乎。然若谓明德之外别有四德则不可。故朱子答或人明德合是性合是心之问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又曰。此两个说。著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则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是非之心。又曰。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朱子之论四德明德之同异。若是精详。而高明则直以明德与四德看作一物。而不知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窃为高明惜之也。
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统而言之。则仁义礼智。以其发见而言之。如恻隐羞恶之类。以其实用言之。如事亲从兄。是也。此非以心统性情行事而言者乎。然若谓明德之外别有四德则不可。故朱子答或人明德合是性合是心之问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又曰。此两个说。著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则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是非之心。又曰。心与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朱子之论四德明德之同异。若是精详。而高明则直以明德与四德看作一物。而不知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窃为高明惜之也。高明以朱子意虽诚了。又不可不正其心之说。为指一念之诚。而非指十分之诚。此有所不然者。大学诚意章。既言慎其独。又言心广体胖。慎独即是工夫。而心广体胖。乃其功效也。则此非诚意之十分善者乎。然而又继言正心工夫。而朱子于其章下注曰。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此其语意。岂非以诚意为十分尽善。而犹不可不复加正心工夫之谓耶。来谕所谓有一分工夫则有一分功效。有十分工夫则有十分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3H 页
 效者。斯诚至言也。然而正心诚意地头少异。不可曰诚意有一分工夫。而正心有一分功效。诚意有十分工夫。而正心有十分功效也。何以明之。朱子之言曰。心言其统体。意是就其中发处。正心如戒惧不睹不闻。诚意如谨独。(朱子说止此。)夫谨独所以遏人欲也。戒惧所以存天理也。欲存天理者。不可不先遏人欲。然若以遏人欲有十分工夫。谓存天理有十分功效。不复加戒惧工夫则可乎。以是推之。则意诚后。犹不可无正心工夫。可知也。
效者。斯诚至言也。然而正心诚意地头少异。不可曰诚意有一分工夫。而正心有一分功效。诚意有十分工夫。而正心有十分功效也。何以明之。朱子之言曰。心言其统体。意是就其中发处。正心如戒惧不睹不闻。诚意如谨独。(朱子说止此。)夫谨独所以遏人欲也。戒惧所以存天理也。欲存天理者。不可不先遏人欲。然若以遏人欲有十分工夫。谓存天理有十分功效。不复加戒惧工夫则可乎。以是推之。则意诚后。犹不可无正心工夫。可知也。所谓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之心字。固是经文章句心者身之所主之心也。心何尝有二哉。但心之体用。初非两物也。心则一。而自其静者言之。则体也。自其动者言之则用也。方其静也。喜怒哀乐未发。而真性浑然。无所偏倚。则此所谓中也大本也。于此时节。岂有正不正之可言也。及其动时。喜怒哀乐始发。发而中节。则所谓和也达道也。此为心得其正也。方发之际。或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有所偏著而不中节。则此为心不得其正也。苟知有所之为病。而能排去之。则动者静而复其体也。此则所谓正心也。故心字未尝不包体用。而其得正与不得正。则乃在用处。而不在其体也。窃详高明以体与用看作两项物事。故曰心之所感之事已去后。体固当正。为忿𢜀等之所留。不得其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3L 页
 云云。则此分明以体用分作两物。而谓此为彼害而不得其正之意也。朱子章句及或问之意。决不如此。愿更加体察焉。
云云。则此分明以体用分作两物。而谓此为彼害而不得其正之意也。朱子章句及或问之意。决不如此。愿更加体察焉。答郑竹溪(栽)
恋德方深。忽承惠状。慰释如何。况满纸缕缕。仰认赤心为学之意。尤用敬服。第执礼过恭。见待过分。是岂如秀浅陋者之所可堪者哉。反复再三。愧怍无已。秀虽尝幸侍先生君子之侧。得闻人生斯世。非学问无以为人之理。而有意此事。为日已久。惟其禀质灭裂。躬行不力。年逾五十而无闻则已矣。何所复望。然犹欲得强辅。相与切磋。以遂朝闻夕死之愿。而不得其人。近因叔经之相从。得闻左右承慈闱之至教。早有志于圣学。已倾心于未见之前。何幸今秋。又遂既见之愿。三日从游。益知其有甘白之质。不胜喜幸。敢以所闻于师友者。勖之矣。高明乃不以人废言而受用之。今而后。吾得免夫失人失言。而窃自幸其庶遂切磋之愿也。所谕八个病痛。益见自省之审密。若其对證之药。则朱子已言之矣。其答孙季和书曰。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弃。不要思前算后。庶能矫革。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此岂非神丹圣药乎。惟左右勿疑而顿服。则得效神速矣。秀之愚。亦尝得一经验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4H 页
 方于小学书中矣。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一句。试之大病小疾。无所不效。此则左右方读小学。想已见得也。林馨汝之质美。诚如来谕。愿相摄以威仪。以共济此事也。
方于小学书中矣。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一句。试之大病小疾。无所不效。此则左右方读小学。想已见得也。林馨汝之质美。诚如来谕。愿相摄以威仪。以共济此事也。答郑竹溪
大小宗图附注云亲尽则请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尽者祭之。既曰亲尽。则其玄孙之已死可知也。又曰就伯叔位服未尽者祭之。则于此尤见其据五代孙而言之也。递迁条云云。意亦如此。来示云云。恐未免局滞也。
告事条。生子满月而见。满月看作满三月者。来论尽好。先贤所谓满一月者。未知其何所据也。
祭田条。亲尽则为墓田。宗子主之云者。与递迁条大宗主其墓田之说同也。所谓诸位迭掌者。恐是二世以下亲尽之墓田。其位之宗子主之。高祖亲尽之墓田。亦其位之宗子主之之谓也。此亦莫非宗子主之。而其曰迭掌者。以其小宗非一故云然也。非谓庶子孙迭相主之也。如何。
虞祭亚献四拜。何以疑之。初献亚献。虽有先后之异。而东酌牺尊。西酌罍尊。乃是男女共为之礼。则其行夹拜。不亦可乎。告生子条。主妇抱子再拜。以其代拜故也。其所以或再或四。各有其义。恐无可疑。
晨谒。家礼但云主人。不言诸子。故秀则不敢行之。今承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4L 页
 教。则退,尤两先生之训若此。然则依其言而行之。恐无不可。然如高明之摄主者。则可如此也。若有宗子在。而诸子不顾宗子之有无。辄独行晨谒。则恐非尊宗之义也。沙溪所谓与主人同谒无妨。无主人而独行则不可者。恐是至论也。如何。
教。则退,尤两先生之训若此。然则依其言而行之。恐无不可。然如高明之摄主者。则可如此也。若有宗子在。而诸子不顾宗子之有无。辄独行晨谒。则恐非尊宗之义也。沙溪所谓与主人同谒无妨。无主人而独行则不可者。恐是至论也。如何。参条附注。刘氏所谓遇水火盗贼。则先救遗文。次祠版云者。似失轻重之序。当从家礼本文。
俗节条。荐以大盘。如正至朔日之仪者。以家礼参条注说观之。则似以龛言。然击蒙要诀参礼仪条云每位设馔。以此观之。则家礼本意。亦以位言耶。大抵荐物。逐位各设。义理方稳。
班祔附注及时祭初献注说。则分明以祔位先父食也。然沙溪于辑览云仪节则先献正位毕而次祔位。朱子亦曰祔食之位。古人祭于东西厢。某只设于堂之两边正位。三献毕。使人分献一酌。如学中从祀然。沙溪见得此等文字。所以有当活看之训也。
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南溪礼说云只用于小祥。不可通用于祥禫诸祭。家礼源流。则不言不用于祥禫。愚意欲从源流。
丧中继后者。从 启下文书到家日为闻讣日。四日成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5H 页
 者。有尤翁定论。则偕丧。虽有妻先夫后之异。继后者则当以文书到后四日成服。成服同日。则似当先父也。
者。有尤翁定论。则偕丧。虽有妻先夫后之异。继后者则当以文书到后四日成服。成服同日。则似当先父也。出继之人。所后父禫月未祭。而遭生母丧者。成服后卜日行所后禫。卒哭后行吉祭。来谕得之。先师答人说。与盛说大同小异。谨为录上如左。
陶庵先生答李敏坤书曰。出后于人者。为其本生亲。虽自伸其心丧。而圣人制礼。则只是伯叔父母之服。遭亲丧者。虽有伯叔父母之服。岂有祥禫不可行之理乎。今之致疑者曰。伯叔父母。则无心丧一节。不可比拟。然自伸其心丧者。情也。一断以期服者。礼也。今于变除之大节。其可拘于情而废于礼乎。抑将伸于公而屈于私乎。况所贵乎礼者。为其别嫌也。苟于此等处。不能一视以伯叔父母之服。则恐非所以严一本之义也。议者又以祥后禫前服色为疑。然私亲与所后服。不可错杂。但当待所后服尽后。方可服私服矣。至于吉祭。则事体尤严重。行之无可疑。
内丧成服前。亲厚之人入吊丧人。未知其可否之如何。丧礼置灵座设魂帛立铭旌下云执友亲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而不言内外丧之别。无乃此所谓执友亲厚者。其指吊条司马公所谓与其子为执友。当升堂拜母者耶。若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5L 页
 则其当入吊无疑矣。不然则似为未安。然人之情分。有多少般数。虽未尝升堂。而其亲密有若升堂者。且于丧事。有不可不与丧人面议者。则虽无哭尸之节。而只行吊仪。恐无不可。未知如何。
则其当入吊无疑矣。不然则似为未安。然人之情分。有多少般数。虽未尝升堂。而其亲密有若升堂者。且于丧事。有不可不与丧人面议者。则虽无哭尸之节。而只行吊仪。恐无不可。未知如何。答郑竹溪
家礼成服条入就位朝哭注。入就位。皆指为位条床东之西位。而备要则朝哭注入就位下小注云位次见上。此似指成服条所引士丧礼门外之位。不同如是。今当何从。
备要所以补家礼之未备者。则凡二书不同处。恐当从备要。
祖奠及遣奠。今俗皆兼行上食。此则谬矣。夕上食。依问解祖奠前行之。至于翌日朝上食。当观遣奠早晚而先后之。以下文食时上食。可知其行于途中也。未知然否。
恐当然也。
先妣葬时。朝祖一事不可废。而祖庙则远在湖西。家中所奉。只是舅姑以下之庙也。栽意以为古者谓庙曰祖。虽祢庙。亦可谓之祖矣。以此行之。而或以为古礼有朝祖朝祢之文。舅姑庙不可曰祖。当云请祖庙。未知孰是。
祢庙亦可谓之祖。已有尤庵定论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6H 页
 主人赠。以杂记注以物送死者于椁中见之。则分明是置于棺椁閒隙地也。然今之识礼家。皆置于棺上云。其有可据之文欤。
主人赠。以杂记注以物送死者于椁中见之。则分明是置于棺椁閒隙地也。然今之识礼家。皆置于棺上云。其有可据之文欤。曾以此质之先师。则云当置之棺椁之间。上玄下纁。置之棺上则无义。
父母偕葬。是夺情之事。下棺当依问解先母。而整柩衣铭旌等事。亦系葬具。恐当先母耶。至于赠题。以伸情论之。而当先父耶。
丧服小记。但言先葬者不虞祔。以待后事。而不言其他。则整柩衣铭旌及赠诸节之当行。固无可疑。而题主一节。亦系葬事。不系祭事。则恐亦当先父为之。然此是臆见。不敢质言。
题主后。撤灵座遂行。无辞墓之文。而俗皆为之。虽非正礼。可从之耶。
礼虽不言。以情理言之。则从俗似无妨。
阖门后及进茶后。俗皆俯伏。鄙意拱立为是。如何。
拱立为是。
进茶后浇饭移匙。辞神前合饭盖下匙。礼所不言。而世皆行之。从之无失礼意否。
浇饭一事。非但礼所不言。撤馔后水饭处置甚难。故礼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6L 页
 则不行云。合盖下匙。从俗无妨。故鄙家亦行之耳。
则不行云。合盖下匙。从俗无妨。故鄙家亦行之耳。启门注。祝噫歆告启门三。以文势观之。噫歆而告启门。如告利成者三度。更考曾子问注。祝为噫歆之声者三。以警动神听。乃告之也。此则谓将启门。而只以噫歆告之者三也。当以礼为正。
以曾子问注说观之。则果是先为噫歆之声三。以警动神听。然后乃告以启门。依此行之可也。
设馔。虽有备要。而家各不同。愿见执事所正者。
鄙家设馔。一依备要图。而但鱼肉并用生熟者。违于沙溪之说矣。
葛绖。沙溪,慎斋,尤庵用粗皮。牛溪,南溪用去皮云。何者可从。
变麻受葛。可见古人重麻轻葛之义。故尤翁以为粗葛之轻重。与麻甚相悬。葛轻麻重也。然以今之粗葛观之。则未见其轻于苴麻也。岂或中国之葛。有异于东方故耶。是可疑也。(然而去皮。则恐非仪礼之本义也。如何。)
中衣。丘仪曰。以练熟之布为冠服。牛溪云用白熟布制之。今从之。不为光鲜乎。
古者三年之丧。以绛色饰练服。则以练熟之布为冠服。恐无嫌于光泽也。如何。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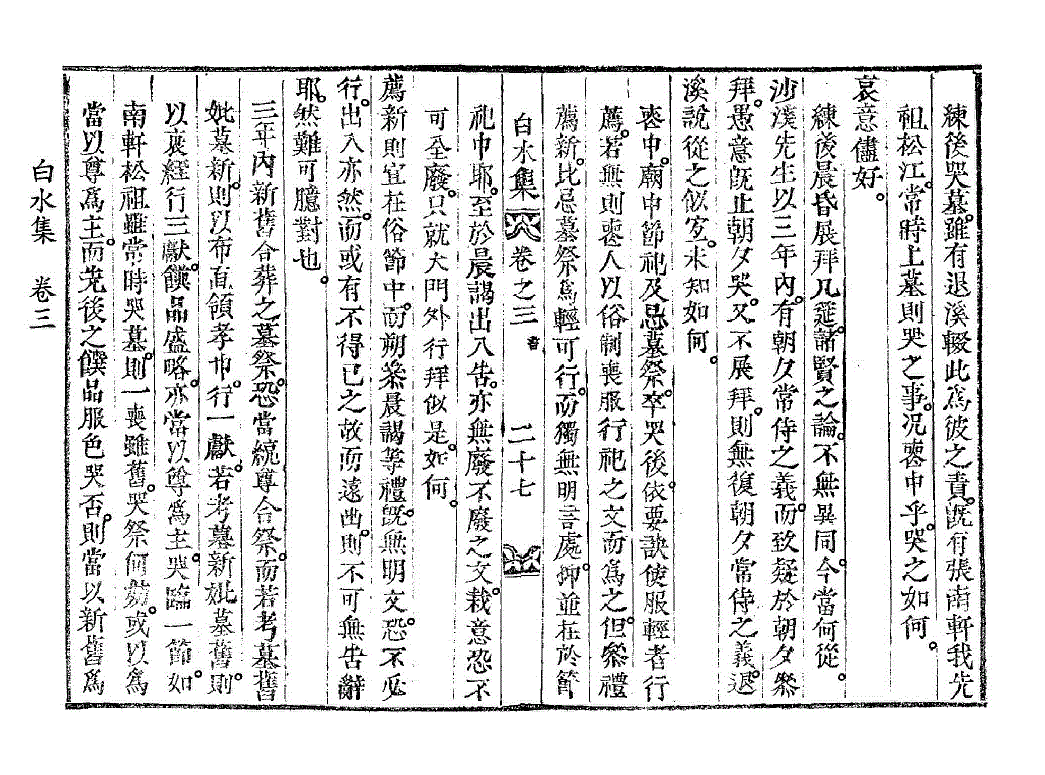 练后哭墓。虽有退溪辍此为彼之责。既有张南轩我先祖松江。常时上墓则哭之事。况丧中乎。哭之如何。
练后哭墓。虽有退溪辍此为彼之责。既有张南轩我先祖松江。常时上墓则哭之事。况丧中乎。哭之如何。哀意尽好。
练后晨昏展拜几筵。诸贤之论。不无异同。今当何从。
沙溪先生以三年内。有朝夕常侍之义。而致疑于朝夕参拜。愚意既止朝夕哭。又不展拜。则无复朝夕常侍之义。退溪说从之似宜。未知如何。
丧中。庙中节祀及忌墓祭。卒哭后。依要诀使服轻者行荐。若无则丧人以俗制丧服行祀之文而为之。但参礼荐新。比忌墓祭为轻可行。而独无明言处。抑并在于节祀中耶。至于晨谒出入告。亦无废不废之文。栽意恐不可全废。只就大门外行拜似是。如何。
荐新则宜在俗节中。而朔参晨谒等礼。既无明文。恐不必行。出入亦然。而或有不得已之故而远出。则不可无告辞耶。然难可臆对也。
三年内新旧合葬之墓祭。恐当统尊合祭。而若考墓旧妣墓新。则以布直领孝巾。行一献。若考墓新妣墓旧。则以衰绖行三献。馔品盛略。亦当以尊为主。哭临一节。如南轩松祖虽常时哭墓。则一丧虽旧。哭祭何妨。或以为当以尊为主。而先后之馔品服色哭否。则当以新旧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7L 页
 主。何见为是。新墓若从而省之。则祝亦不可用耶。
主。何见为是。新墓若从而省之。则祝亦不可用耶。愚尝闻之陶庵先生曰。三年内异几。明有礼文。神主未合位之前。墓所并祭甚未安。凡合葬之墓须各行。而并有丧则先重后轻而各服其服。哭而行事。若父先亡。母祭三年内。则以平凉子直领。不哭而先祭父。改以衰麻。哭而祭母。若母先亡。父丧三年内。则祭父毕。但去杖脱绖。不哭而行母祀。似为合宜。
又闻松江云三年内墓祀。叔献及砺城。皆以单献为是。(注墓祀指新丧。)松江之训如是。而哀则以三献为说。岂愚之所闻失是邪。抑松江此说。不载文集。而见于他书耶。是可疑也。
附注奔丧。凡丧父在父为主注。与宾客为礼。宜使尊者。此尊者非为为主之父而别尊耶。
以文势观之。此尊者非为主之父也。
舅主妇丧。服问丧服疏皆云不主庶妇。奔丧礼记集说皆云主庶妇。彼此径庭。莫的所从。未知何以则得礼耶。
主庶妇不主庶妇之不同者。以同宫异宫之不同也。而问解续卷云如今人父子虽异宫。父在则子不各主其丧。先师陶庵先生亦曰。异宫之义。古今制殊。只当以父在父为主为经也。
子与其妻及孙与其妻之丧。无论嫡庶与同宫异宫。当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8H 页
 一主于父在父为主之文。祖在则其父虽在。祖主之。父在则父主之。无所妨碍。未知如何。
一主于父在父为主之文。祖在则其父虽在。祖主之。父在则父主之。无所妨碍。未知如何。当然也。
主妇有疑。本注既曰亡者之妻。无则主丧者之妻。下文更无分别。而问解曰。初丧则亡者之妻为主妇。虞以后。丧者妻为主妇。未知何据。
问解亡者之妻为主妇。下曰时未传家于冢妇故也。主丧者。当为主妇。下曰祭祀之礼。必夫妇亲之故也。其下又引张子说以为證。此非所据耶。
馀有服者。不言去冠。而问解为生父母及祖父母与妻丧。去吉冠云。而伯叔父母则不言。然则伯叔父母丧。着吉冠自如其可乎。重服有脱网巾者。此则愚意恐失。如何。
以经文妻子妇妾皆去冠云观之。则虽祖父母妻丧。似无去冠之礼。以问解所云推之。则虽伯叔父母丧。不去冠。亦似未安。而尤庵云期服于初终。崔氏既有白巾之文。则或布或绵或纸。何所不可。此非后学之所当遵行者乎。网巾。南溪云只有服者。不脱网巾。但生父母丧。则亦似脱之。此言恐得之。如何。
陈袭条。幅巾,充耳,深衣,大带,履皆言数。而独于幎目,握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8L 页
 手则不言数何耶。幎目用一无疑。虽不言数可也。握手则不为名言。则一二可疑。是以人或以用一为疑无怪也。刘氏握手注文势简涉。虽难读。亦不无用一之疑。愚意非用一为当求其文势。有此不当之疑矣。且揽与掌后节。同耶异耶。刘氏注。伏望句教也。
手则不言数何耶。幎目用一无疑。虽不言数可也。握手则不为名言。则一二可疑。是以人或以用一为疑无怪也。刘氏握手注文势简涉。虽难读。亦不无用一之疑。愚意非用一为当求其文势。有此不当之疑矣。且揽与掌后节。同耶异耶。刘氏注。伏望句教也。握手虽不言数。而其当用二无疑也。故备要添二字。刘说奇高峰有所辨释。录上如左。奇高峰曰。按刘氏引疏不完。使人难晓。记疏云握手一端绕掔还从上自贯反。与其一端结之者。按上文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里今亲肤。据从手内置之。长尺二寸中掩之手才相对也云云。此乃疏家引经释记。故其言如此云者。指注也。上文指经也。今指记也。据谓据以为言。盖注曰长尺二寸。而记又曰。里亲肤。乃据其从手内。置之中掩之而言也。今字据字。皆为虚字斡旋。而刘氏所引。以今作令。而去注文一节及上文二字。故据字不见来历。而手才相对四字。无所著落。宜乎后学之疑惑也。今宜正之。纁下有里字。而削去今据两字及手才相对也五字。则文简而意明矣。○揽。韵会脘。注乌贯切。掌后节也。右见家礼辑览。今按字汇。揽音悭。坚也固也。此则与辑览所引不同疑。
勒帛。以上文见之。似是代带者。而备要注束经至膝。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9H 页
 据否。
据否。勒帛。如小学偪屦之偪相似。如今之行縢。初非带名也。
沐浴条。主人以下。皆出帷外。亲切无如主人。而出外者。何也。
主人以下皆出帷外者无他。以帷内狭窄。恐妨于侍者之役事而然也。
徙尸注馀言在堂仿此。此义未晓。
馀言在堂者。谓如小敛条迁尸床于堂中。大敛条举棺入置堂中少西之类。
袭无结纽之文。不结之为有据耶。
不结无据。结之恐当。
陈袭注。不别言女丧。然则女丧。亦可通用此袭具邪。既用深衣大带。则其制当如男丧所用。而首则用掩。未知如何。
深衣者。在古为贵贱文武男女吉凶通用之服。故尤庵云妇人亦当用深衣。我陶庵先生曰。带亦当用深衣之带。而至于幅巾。则无男女通用之文。故备要云女丧当用掩。
饭含。檀弓饭用米贝。又注饭则含也。以用米故谓之饭含也。礼运饭腥注。以生稻米为含也。杂记大夫饭五贝。士三。其义分明是含饭也。而闻礼家。或以饭米含珠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99L 页
 之。家礼谚解。亦且饭且含释之。此何据。
之。家礼谚解。亦且饭且含释之。此何据。问解所引礼经诸说末段曰。本注谓饭含也。是即以饭为含矣。参之礼运曰饭腥。谷梁氏谓贝玉曰含。则二者虽皆为口实。而用则不同。谓之饭含则可。谓含饭也则不可。礼家之或以饭米含珠看之。家礼谚解之且饭且含释之者。恐本于此也。
士丧礼。亲者襚。庶兄弟襚。愚意亲者与庶兄弟。似无分别而各言之。未知亲者如何亲者。庶兄弟如何兄弟邪。
亲者谓大功以上同财者也。庶兄弟。谓同姓众兄弟也。详见士丧礼注疏。
铭旌。六品以下七尺。无官者几尺为度耶。恐可用礼穷则从下之文否。
檀弓疏铭士长三尺。大夫五尺。诸侯七尺。天子九尺。无官者恐当三尺之制。如何。
堂下官妻无封帖。朝例也。既未受帖。而铭旌书某封。恐不可。无实职而有资级者之妻。礼家亦许称封如何。
虽无封帖。而从夫实职。礼则然矣。乌可以无封帖而不书乎。至于无实职而只有资级者之妻。则恐不当书封号。礼家亦许之意。愚不知也。
小敛衾用复者。复恐是表里而已。备要注意亦明是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0H 页
 絮矣。而大记注。复有绵纩者。何者为得。
絮矣。而大记注。复有绵纩者。何者为得。复。补注挟也。挟字汇同袷。袷音夹。衣无絮也。以此观之。则大记注可疑。而来示备要注意是充絮云者。亦未可晓。
设奠具注。置奠馔及盏注。馔则固也。而盏注既设于设灵座时。而以此又设之。岂非叠床者乎。
盏注不必用一。且设灵座时。设盏注于灵座前卓子也。此所谓盏注。则设阼阶东南之卓子者也。处所既异。尤不可疑也。
括发免髽注不明白。愚意以下文斩衰者括发。齐衰以下皆免之语及备要括发具注。括发只言斩衰。而不及齐衰之事见之。括发专言斩衰。而免是齐衰。不须论也。布头𢄼。以本注以布之语及斩衰条。妇人布头𢄼之说。与书仪男子斩衰亦以布为头𢄼之文见之。似通男女而斩衰并言也。髽麻则恐举重而言之。齐衰用布。亦可推之。但丧服小记注括发母死亦然。此说备要亦补入。问解又云当以小记为准。然则为母亦当括发。未知如何。
细看小记。拜宾以前则为父为母皆括发。拜宾竟。子即堂下位之时。父丧则犹括发而踊。母丧则不复括发。而著布免以踊。更详之如何。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0L 页
 设小敛床注。或颠或倒。颠倒一意而重言之。何邪。
设小敛床注。或颠或倒。颠倒一意而重言之。何邪。古语云走不视地者颠。衣不举领者倒。由是观之。颠与倒。亦当有别。
自袭奠。以至朝夕奠。脯醢当何左右耶。备要图袭奠。左醢右脯。迁袭奠。左脯右醢。一脯醢而设迁之不同。何邪。
南溪云。左脯右醢。乃象生时之意。恐此为是。其右脯左醢者。似是写误致然。
括发条。温公注冠梳之梳。何谓耶。
去梳。似是不栉之意。然不敢质言。
小敛奠具。只云奠馔。而无所名言。当如袭奠而设之。备要小敛奠具。有果何据。此可从之否。
家礼袭奠二言脯醢。而小敛奠。特加一馔字。故备要以酒果脯醢之类释之。其当从无疑。
袭之冒。杨氏所补而古礼也。小敛之舒绢叠衣。原注而今礼也。窃观上下文势。各为一礼。行礼家只当取舍。而不可并用也。又思之。设冒之后。又藉首补肩夹胫之事。似未得便宜。若用冒。则未掩面亦难。如何。
来谕诚然。未掩面一节。虽不设冒。事势有行不得者。故礼家多依仪礼卒敛云。
还迁尸床之还字。问解有两义。而愚意或说为胜如何。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1H 页
 愚则从退溪说。
愚则从退溪说。举棺入注。先迁灵座及小敛奠于傍侧。似于堂上傍侧迁之。而备要图无迁灵座处。撤敛奠。亦在于阶下者。何耶。
备要图无迁灵座处。恐是偶然。阶下撤敛奠。与迁奠不同。非所可疑也。
苴黎墨色竹色。本不黎墨而曰苴者何耶。
会成曰。苴杖自死之竹也。此说恐是盖自死之竹。故有黎墨之色也。
屦粗麻为之。今用之有据。而世俗皆用草鞋。若见用麻者。必非之。从俗用草可乎。
世俗之用稿鞋。出自备要。则当从之。
布头𢄼一。而男子用于括发。妇人用于成服者。何耶。
备要括发免髽之具。布头𢄼即总。所以束发者。图式妇人以六升布为总。由是观之。则括发免髽之时。妇人之亦用头𢄼可知也。
妇人衰裳而杖。仪礼也。大袖长裙不杖。家礼也。近见妇人用衰裳者仅有。而皆是用大袖长裙而又有杖。岂非两违于仪礼,家礼乎。
家礼之用书仪服制。妇人皆不杖。与问丧,丧大记,丧服小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1L 页
 记不同。杨氏恨未得质正云。则妇人虽用大袖长裙者。恐无不杖之义。如何如何。
记不同。杨氏恨未得质正云。则妇人虽用大袖长裙者。恐无不杖之义。如何如何。家礼妇人服无绖带。既明矣。又可以小祥设练服注说證之矣。愚意用大袖长裙则不可杖且绖带。若依仪礼衰裳而杖。则真可以绖带。未知如何。
备要小祥之具。妇人服制。首绖以葛为之。腰绖除之。用长裙之制则截之。以此推之。则虽用大袖长裙。亦有绖带可知也。如何。
袷。杨氏言之。而其施之之法不详。至备要注然后乃明矣。然施袷未见如备要之制。栽亦略知丧服截制法。而施袷则从简有别法。其法用布长广如其制。纵摺为三重。下一重展之。上自二重。其下一重两端摺记处。各截八方四寸而不除去。其两端不除去者。分摺相向。亦一重。以此加领里。未知不悖耶。
哀之截法亦妙。易曰。天下殊涂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此之谓欤。
袂必属幅。丧服注。属。犹连也。连幅谓不削。然则衣袂相连。不去边幅一寸。而内不削。外不削。无表里缝之耶。
丘仪不削。谓随其布幅。不用剪裁修饰。沙溪曰。属幅。属连其幅。不杀削之。全用二尺二寸也。削幅则各除左右一寸。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2H 页
 而斜缝之。非谓削割之也。此属幅削幅之别也。(见于辑览者如此。而其详。则愚亦未达。恐只是用全幅。而不加修饰之意也。)
而斜缝之。非谓削割之也。此属幅削幅之别也。(见于辑览者如此。而其详。则愚亦未达。恐只是用全幅。而不加修饰之意也。)仪礼。斩衰菅屦。非屦也。菅菲为草之一物耶。抑为屦之异名耶。下文已沤为菅。菅何以沤之耶。外饰文义则收其馀末向外也。而文法则外面去恶取美也。可怪而不足辨也。齐衰疏屦。以文见之则同一草也。何有斩衰之别乎。备要注。疏屦。藨蒯之类。藨蒯未知何物耶。斩衰。既用已沤之菅。则齐衰疏屦。似有比沤尤精之道。何以为之。疏读如不熟之疏。其以不熟之疏读之云耶。草体举恶举草总称。亦何谓邪。
以字汇所释观之。则菅与菲。各异也。家礼注云菅菲外纳。则周公时谓之屦。子夏时谓之菲。以此观之。则屦或谓之菲也。菅如今之蒲草。沤谓渍水外饰。饰字纳之误耶。外纳南溪云士丧礼注。纳。收馀也。今之织屦者。皆以收馀入内。而使外面便美。则岂不与菅屦相反耶。字汇。藨音殍。草可为席。蒯草名。左传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蒯与菅。皆苕也。黄华者。即蒯也。白华者。即菅也。读如不熟之疏。来示然矣。菅草名。故曰言菅以见草体。举其恶貌也。疏非草名。而只是粗粗之意。故曰举草之总称也。(疏屦之草。不止于菅故也。)
为长子。父在服三年耶否。愚按丧服疏。父母为长子。本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2L 页
 为先祖之正体。无压降义。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以此观之。为长子。父虽在不敢降服明矣。未知如何。前闻少论学者李养源宰和顺时。遭长妇丧。以父在降服大功云。其父之为长孙妇。姑在降服。而李养源之降。愚则未知。未知有何据耶。愿闻之。
为先祖之正体。无压降义。故不得以父在而屈也。以此观之。为长子。父虽在不敢降服明矣。未知如何。前闻少论学者李养源宰和顺时。遭长妇丧。以父在降服大功云。其父之为长孙妇。姑在降服。而李养源之降。愚则未知。未知有何据耶。愿闻之。问解。沙溪先生答同春父在则为长子不服三年否之问曰。父在则为长子不服三年。疏家说详之。下方引丧服疏。周之道。有嫡子无嫡孙。嫡孙犹同庶孙之例云云以證之。李和顺之以父在降服其长孙者。恐以此为据也。故愚则闻其说。而不以为非。今观哀引丧服疏说。则父虽在。为长子不降服亦明矣。愿博考广询。更示折衷之论。如何。
备要斩衰条。妇为舅。夫承重则从服注。沙溪曰。但其夫未及承重而早死者。则又未知如何处之也。此系大节目。而未有断定之论。今之遭此礼者多有之。而何以为处。愚何敢质言于沙溪未定之变礼。而然此亦可以属从者虽没也服之说为据。此说岂可独用于夫承重者乎。僭汰悚仄。幸明教也。
沙溪于问解论此事曰。退溪先生所引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一段。实是的确明證。恐不容有他议。此非沙溪先生已定之论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3H 页
 古礼大夫士服制。固有等级。而家礼去大夫存士以同之。无曰士曰大夫。而惟于齐衰三年条注曰。士之庶子为其母缌麻条注曰。士为庶母。杨注亦曰。大夫为贵妾。士为妾有子者。何耶。
古礼大夫士服制。固有等级。而家礼去大夫存士以同之。无曰士曰大夫。而惟于齐衰三年条注曰。士之庶子为其母缌麻条注曰。士为庶母。杨注亦曰。大夫为贵妾。士为妾有子者。何耶。家礼。乃参酌古今之礼而成之者也。故不纯用仪礼。贵贵底礼数。而至于此等处。不可全无贵贱之别。故本注曰士云云。而杨注亦曰大夫云云士云云。愚见如是。未知如何。
齐衰三年条大注。既有嫡孙父卒为祖母之文。而杨注又增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未知其义不叠床耶。
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丧服图式注。祖父卒时父在。己虽为祖期。今父没。祖母亡。亦为祖母三年。由是观之。则杨注。恐不与大注叠床也。
妻为夫之养母慈母。依沙溪言从服。而夫三年。则妻从服三年。夫期则妻从服期乎。抑或如古礼从服而降一等乎。然则夫之君师。亦可从服否耶。
沙溪之言曰。继母嫡母。与生母无异。故不别言之。养母慈母。亦从夫服无疑也。详其语意。则似谓当从夫服齐衰三年也。为夫之君从服。经有明文。至于为师从服。不见经传。
子为父后。则为出母嫁母无服之意。当于降服。为嫁母出母下。略其文曰。而为父后则无服。如此则文简义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第 103L 页
 而何以烦其文。而在于义服中耶。其下继母出则无服也。当于齐衰三年条为继母下。略其文曰而出则无服。何以在于杖期中。而无所着落耶。
而何以烦其文。而在于义服中耶。其下继母出则无服也。当于齐衰三年条为继母下。略其文曰而出则无服。何以在于杖期中。而无所着落耶。愚按杖期条。自嫡孙父卒祖在为祖母也。至夫为妻也以应服杖期者言之也。自子为父后。则为出母以下。应服杖期。而变为无服者言之也。条理分明。无复可疑也。
备要杖期条。嫡孙父卒祖在为祖母注。沙溪曰。嫡孙父卒祖在为母。疑亦蒙祖在为祖母。此虽非质言。而盖尝疑之矣。未知世之遭此礼者。何以处之。愚意沙溪之言。恐未安。此说无礼经明文。而又有祖不压孙之文。岂可遽从降服之例耶。
沙翁说。尤,春两先生皆不从。南溪。亦以为未安云。
备要斩衰条。父为嫡子注。引杂记曰。为长子杖。则其子不以杖即位。以此观之。为母杖者。亦当避父。如何。
似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