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x 页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书
书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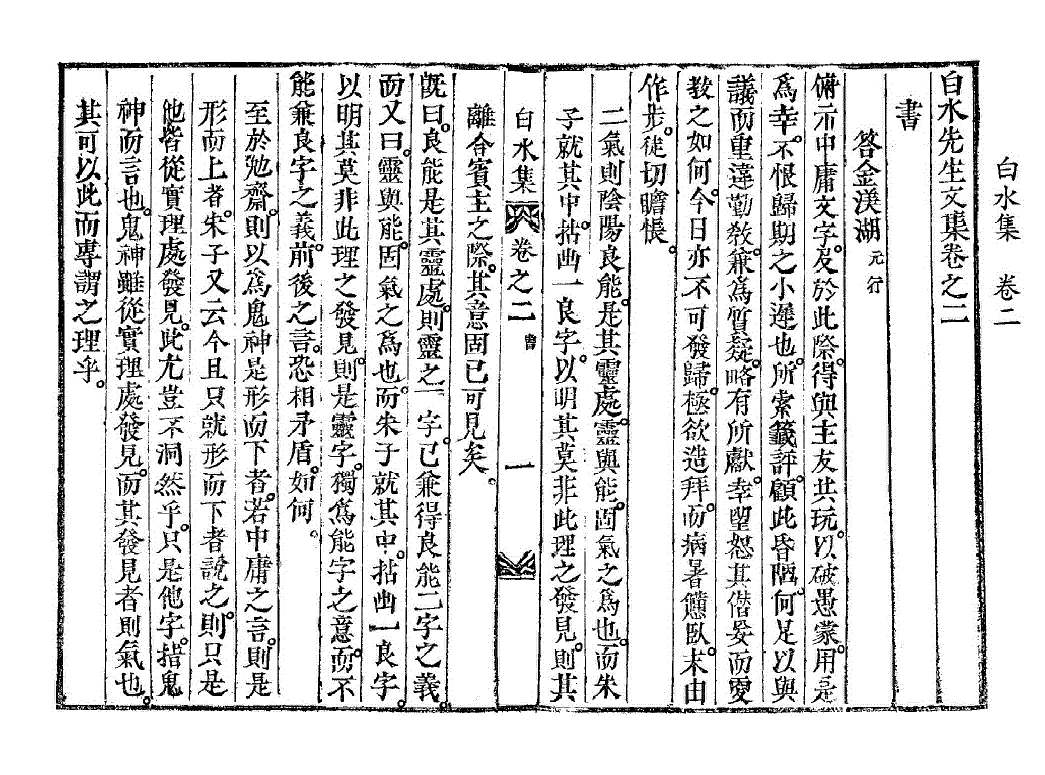 答金渼湖(元行)
答金渼湖(元行)俯示中庸文字。及于此际。得与主友共玩。以破愚蒙。用是为幸。不恨归期之小迟也。所索签评。顾此昏陋。何足以与议而重违勤教。兼为质疑。略有所献。幸望恕其僭妄而更教之如何。今日亦不可发归。极欲造拜。而病暑惫卧。末由作步。徒切瞻怅。
二气则阴阳良能。是其灵处。灵与能。固气之为也。而朱子就其中。拈出一良字。以明其莫非此理之发见。则其离合宾主之际。其意固已可见矣。
既曰。良能是其灵处。则灵之一字。已兼得良能二字之义。而又曰。灵与能。固气之为也。而朱子就其中。拈出一良字。以明其莫非此理之发见。则是灵字。独为能字之意。而不能兼良字之义。前后之言。恐相矛盾。如何。
至于勉斋。则以为鬼神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则是形而上者。朱子又云今且只就形而下者说之。则只是他皆从实理处发见。此尤岂不洞然乎。只是他字。指鬼神而言也。鬼神虽从实理处发见。而其发见者则气也。其可以此而专谓之理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2L 页
 此鬼神。正与鸢鱼是一般意思。鸢鱼之飞跃。是气之为也。而其所以飞所以跃。则理也。故不害用费隐字。况此鬼神虽若主于气而理实在其中矣。今以费隐明之者。又何不可耶。
此鬼神。正与鸢鱼是一般意思。鸢鱼之飞跃。是气之为也。而其所以飞所以跃。则理也。故不害用费隐字。况此鬼神虽若主于气而理实在其中矣。今以费隐明之者。又何不可耶。朱子所谓鬼神也是鸢飞鱼跃意思者。鸢飞鱼跃一段。即所以明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者。而鬼神之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亦是此理流动充满之意也。然则高明所谓一般意思者。诚是矣。然鸢鱼之飞跃。是气之为也。而其所以飞所以跃则理也。故不害用费隐字。此段语。恐未免不备之叹。何者。上而鸢下而鱼。理无不在。此则费也。而其所以然则非见闻所及。此则隐也。今高明以费隐并属所以然。则是其辞可谓备乎。且鸢鱼一段。正所以明费隐。而高明则以为不害用费隐字。不害用三字。不为病乎。况此鬼神虽若主于气。而理实在其中。今以费隐明之者。又何不可耶此一段。亦恐未安。若以理实在其中。谓可以费隐明之。则凡天下之物。何莫非理在其中。而必于鬼神。独以费隐明之乎。鄙见如是。如有未莹。幸更教也。
答金渼湖
族侄赫回。伏承惠复书。迄庸披玩。不任慰感。寒暖不常。伏惟履道起居一向万安。区区瞻慕。夙宵靡弛。金生声律孝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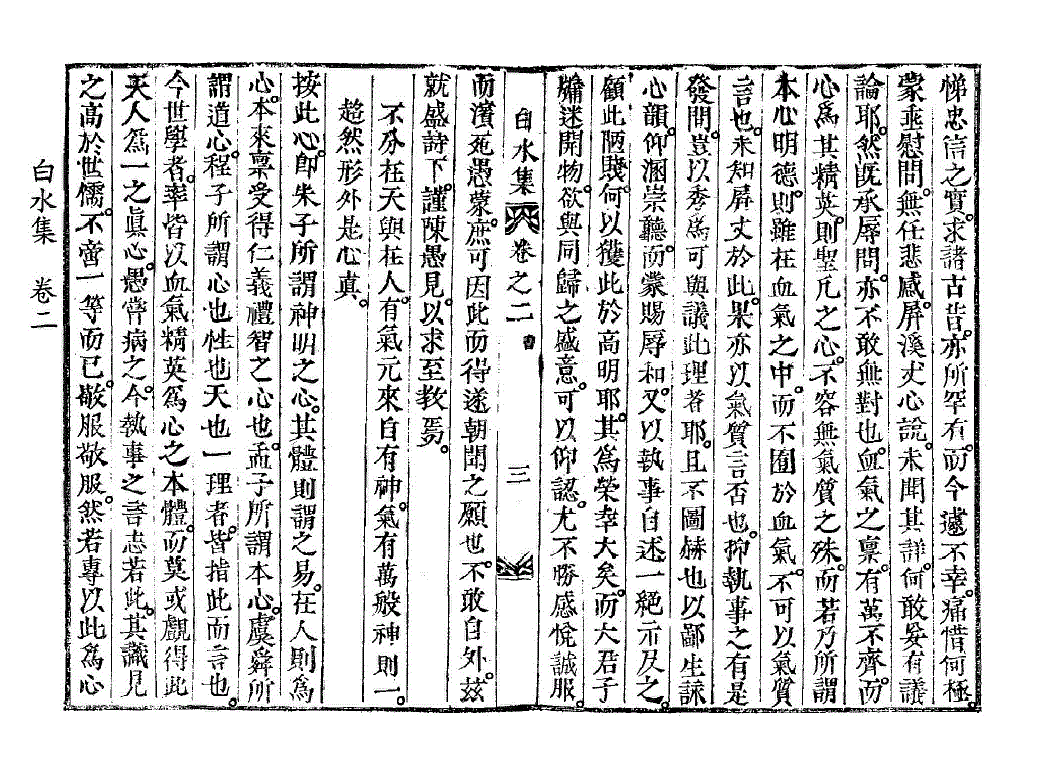 悌忠信之实。求诸古昔。亦所罕有。而今遽不幸。痛惜何极。蒙垂慰问。无任悲感。屏溪丈心说。未闻其详。何敢妄有议论耶。然既承辱问。亦不敢无对也。血气之禀。有万不齐。而心为其精英。则圣凡之心。不容无气质之殊。而若乃所谓本心明德。则虽在血气之中。而不囿于血气。不可以气质言也。未知屏丈于此。果亦以气质言否也。抑执事之有是发问。岂以秀为可与议此理者耶。且不图赫也以鄙生咏心韵。仰溷崇听。而蒙赐辱和。又以执事自述一绝示及之。顾此陋贱。何以获此于高明耶。其为荣幸大矣。而大君子牖迷开物。欲与同归之盛意。可以仰认。尤不胜感悦诚服。而滨死愚蒙。庶可因此而得遂朝闻之愿也。不敢自外。玆就盛诗下。谨陈愚见。以求至教焉。
悌忠信之实。求诸古昔。亦所罕有。而今遽不幸。痛惜何极。蒙垂慰问。无任悲感。屏溪丈心说。未闻其详。何敢妄有议论耶。然既承辱问。亦不敢无对也。血气之禀。有万不齐。而心为其精英。则圣凡之心。不容无气质之殊。而若乃所谓本心明德。则虽在血气之中。而不囿于血气。不可以气质言也。未知屏丈于此。果亦以气质言否也。抑执事之有是发问。岂以秀为可与议此理者耶。且不图赫也以鄙生咏心韵。仰溷崇听。而蒙赐辱和。又以执事自述一绝示及之。顾此陋贱。何以获此于高明耶。其为荣幸大矣。而大君子牖迷开物。欲与同归之盛意。可以仰认。尤不胜感悦诚服。而滨死愚蒙。庶可因此而得遂朝闻之愿也。不敢自外。玆就盛诗下。谨陈愚见。以求至教焉。不分在天与在人。有气元来自有神。气有万般神则一。超然形外是心真。
按此心。即朱子所谓神明之心。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为心。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也。孟子所谓本心。虞舜所谓道心。程子所谓心也性也天也一理者。皆指此而言也。今世学者。率皆以血气精英为心之本体。而莫或觑得此天人为一之真心。愚尝病之。今执事之言志若此。其识见之高于世儒。不啻一等而已。敬服敬服。然若专以此为心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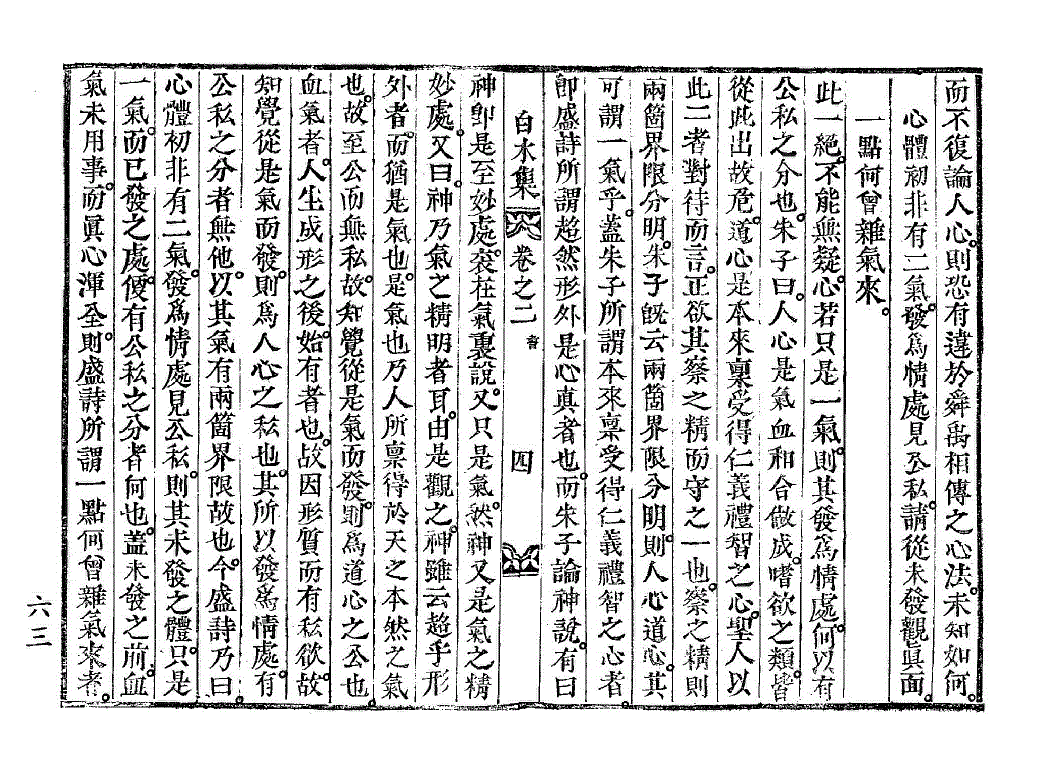 而不复论人心。则恐有违于舜禹相传之心法。未知如何。
而不复论人心。则恐有违于舜禹相传之心法。未知如何。心体初非有二气。发为情处见公私。请从未发观真面。一点何曾杂气来。
此一绝。不能无疑。心若只是一气。则其发为情处。何以有公私之分也。朱子曰。人心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圣人以此二者对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朱子既云两个界限分明。则人心道心。其可谓一气乎。盖朱子所谓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者。即盛诗所谓超然形外是心真者也。而朱子论神说。有曰神即是至妙处。衮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又曰。神乃气之精明者耳。由是观之。神虽云超乎形外者。而犹是气也。是气也乃人所禀得于天之本然之气也。故至公而无私。故知觉从是气而发。则为道心之公也。血气者。人生成形之后。始有者也。故因形质而有私欲。故知觉从是气而发。则为人心之私也。其所以发为情处。有公私之分者无他。以其气有两个界限故也。今盛诗乃曰。心体初非有二气。发为情处见公私。则其未发之体。只是一气。而已发之处。便有公私之分者何也。盖未发之前。血气未用事。而真心浑全。则盛诗所谓一点何曾杂气来者。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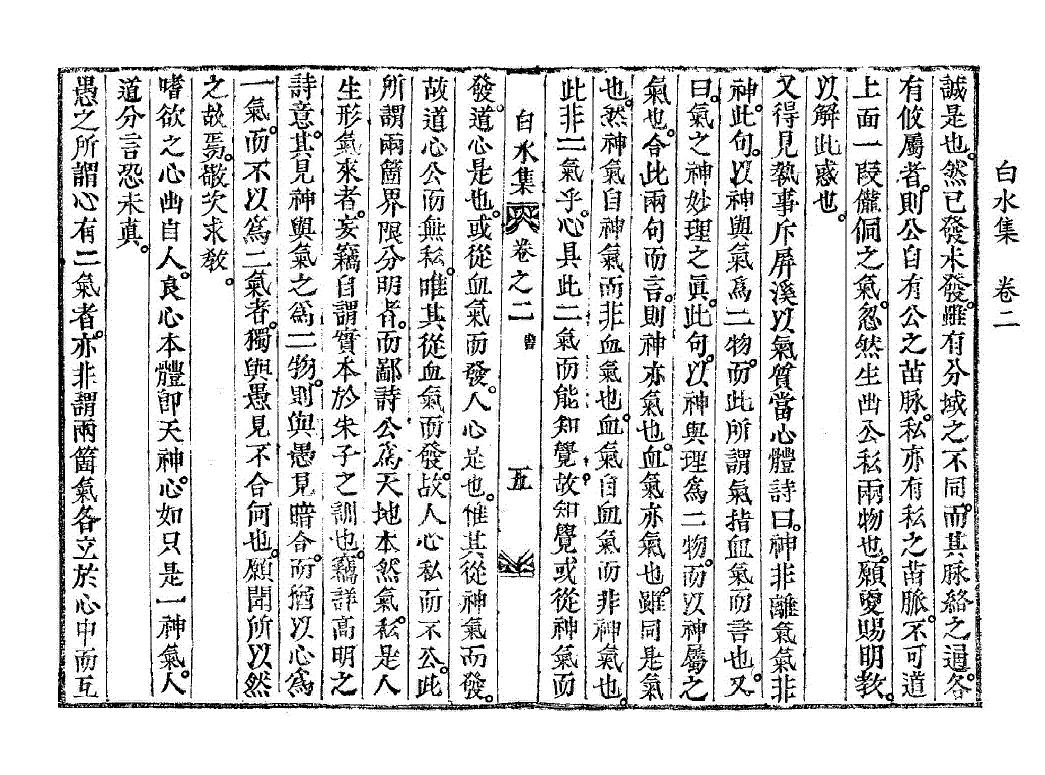 诚是也。然已发未发。虽有分域之不同。而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公自有公之苗脉。私亦有私之苗脉。不可道上面一段儱侗之气。忽然生出公私两物也。愿更赐明教。以解此惑也。
诚是也。然已发未发。虽有分域之不同。而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公自有公之苗脉。私亦有私之苗脉。不可道上面一段儱侗之气。忽然生出公私两物也。愿更赐明教。以解此惑也。又得见执事斥屏溪以气质当心体诗曰。神非离气气非神。此句。以神与气为二物。而此所谓气指血气而言也。又曰。气之神妙理之真。此句。以神与理为二物。而以神属之气也。合此两句而言。则神亦气也。血气亦气也。虽同是气也。然神气自神气而非血气也。血气自血气而非神气也。此非二气乎。心具此二气而能知觉。故知觉或从神气而发。道心是也。或从血气而发。人心是也。惟其从神气而发。故道心公而无私。唯其从血气而发。故人心私而不公。此所谓两个界限分明者。而鄙诗公为天地本然气。私是人生形气来者。妄窃自谓实本于朱子之训也。窃详高明之诗意。其见神与气之为二物。则与愚见暗合。而犹以心为一气。而不以为二气者。独与愚见不合何也。愿闻所以然之故焉。敬次求教。
嗜欲之心出自人。良心本体即天神。心如只是一神气。人道分言恐未真。
愚之所谓心有二气者。亦非谓两个气各立于心中而互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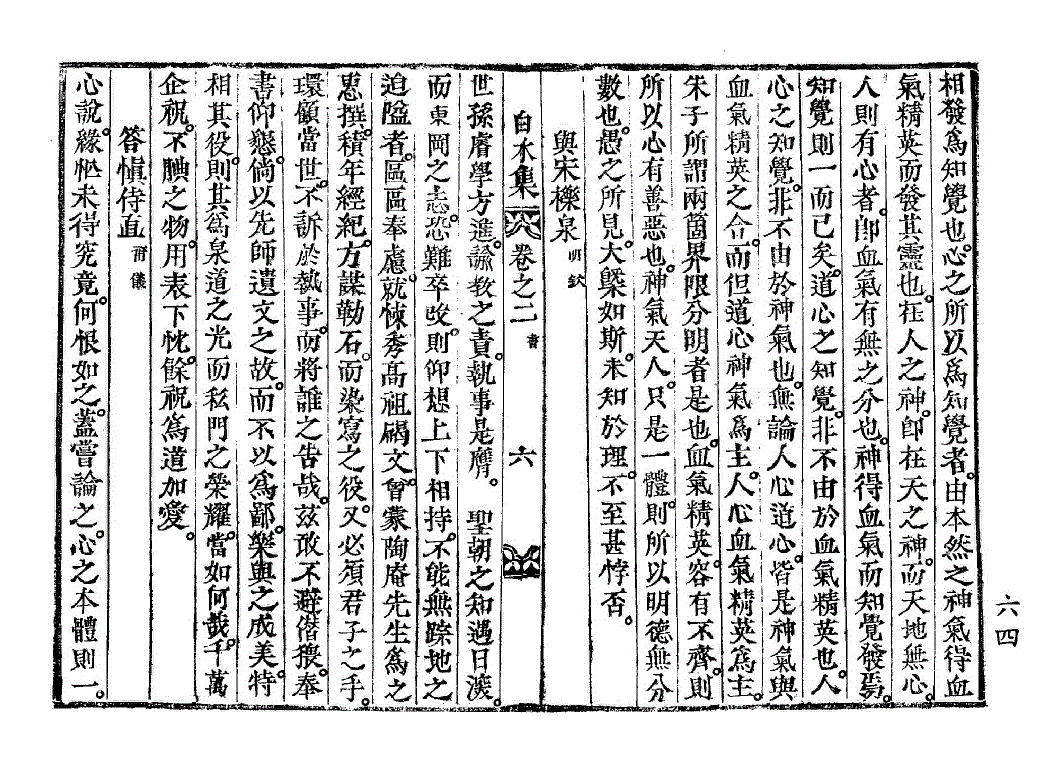 相发为知觉也。心之所以为知觉者。由本然之神气得血气精英而发其灵也。在人之神。即在天之神。而天地无心。人则有心者。即血气有无之分也。神得血气而知觉发焉。知觉则一而已矣。道心之知觉。非不由于血气精英也。人心之知觉。非不由于神气也。无论人心道心。皆是神气与血气精英之合。而但道心神气为主。人心血气精英为主。朱子所谓两个界限分明者是也。血气精英。容有不齐。则所以心有善恶也。神气天人。只是一体。则所以明德无分数也。愚之所见。大槩如斯。未知于理。不至甚悖否。
相发为知觉也。心之所以为知觉者。由本然之神气得血气精英而发其灵也。在人之神。即在天之神。而天地无心。人则有心者。即血气有无之分也。神得血气而知觉发焉。知觉则一而已矣。道心之知觉。非不由于血气精英也。人心之知觉。非不由于神气也。无论人心道心。皆是神气与血气精英之合。而但道心神气为主。人心血气精英为主。朱子所谓两个界限分明者是也。血气精英。容有不齐。则所以心有善恶也。神气天人。只是一体。则所以明德无分数也。愚之所见。大槩如斯。未知于理。不至甚悖否。与宋栎泉(明钦)
世孙睿学方进。谕教之责。执事是膺。 圣朝之知遇日深。而东冈之志。恐难卒改。则仰想上下相持。不能无踪地之迫隘者。区区奉虑。就悚秀高祖碣文。曾蒙陶庵先生为之惠撰。积年经纪。方谋勒石。而染写之役。又必须君子之手。环顾当世。不诉于执事。而将谁之告哉。玆敢不避僭猥。奉书仰恳。倘以先师遗文之故。而不以为鄙。乐与之成美。特相其役。则其为泉道之光而私门之荣耀。当如何哉。千万企祝。不腆之物。用表下忱。馀祝为道加爱。
答慎侍直(尔仪)
心说。缘忙未得究竟。何恨如之。盖尝论之。心之本体则一。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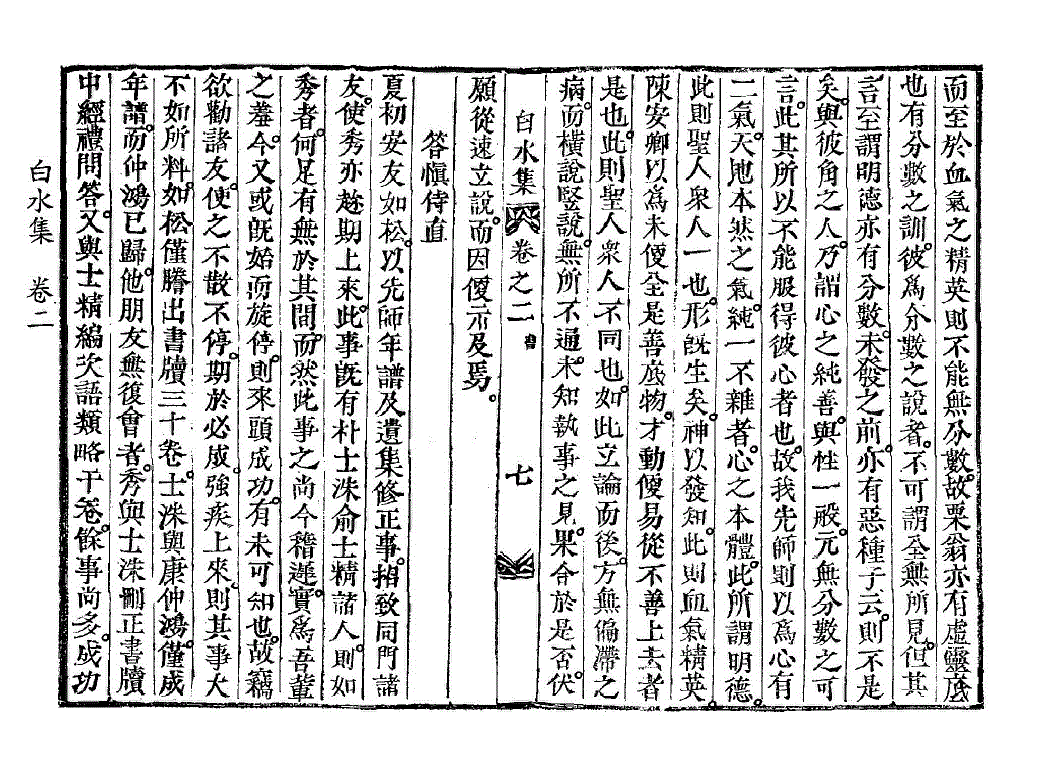 而至于血气之精英则不能无分数。故栗翁亦有虚灵底也有分数之训。彼为分数之说者。不可谓全无所见。但其言至谓明德亦有分数。未发之前。亦有恶种子云。则不是矣。与彼角之人。乃谓心之纯善。与性一般。元无分数之可言。此其所以不能服得彼心者也。故我先师则以为心有二气。天地本然之气。纯一不杂者。心之本体。此所谓明德。此则圣人众人一也。形既生矣。神以发知。此则血气精英。陈安卿以为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者是也。此则圣人众人不同也。如此立论而后。方无偏滞之病。而横说竖说。无所不通。未知执事之见。果合于是否。伏愿从速立说。而因便示及焉。
而至于血气之精英则不能无分数。故栗翁亦有虚灵底也有分数之训。彼为分数之说者。不可谓全无所见。但其言至谓明德亦有分数。未发之前。亦有恶种子云。则不是矣。与彼角之人。乃谓心之纯善。与性一般。元无分数之可言。此其所以不能服得彼心者也。故我先师则以为心有二气。天地本然之气。纯一不杂者。心之本体。此所谓明德。此则圣人众人一也。形既生矣。神以发知。此则血气精英。陈安卿以为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动便易从不善上去者是也。此则圣人众人不同也。如此立论而后。方无偏滞之病。而横说竖说。无所不通。未知执事之见。果合于是否。伏愿从速立说。而因便示及焉。答慎侍直
夏初安友如松。以先师年谱及遗集修正事。招致同门诸友。使秀亦趁期上来。此事既有朴士洙俞士精诸人。则如秀者。何足有无于其间。而然此事之尚今稽迟。实为吾辈之羞。今又或既始而旋停。则来头成功。有未可知也。故窃欲劝诸友。使之不散不停。期于必成。强疾上来。则其事大不如所料。如松仅誊出书牍三十卷。士洙与康仲鸿。仅成年谱。而仲鸿已归。他朋友无复会者。秀与士洙删正书牍中经礼问答。又与士精编次语类略干卷。馀事尚多。成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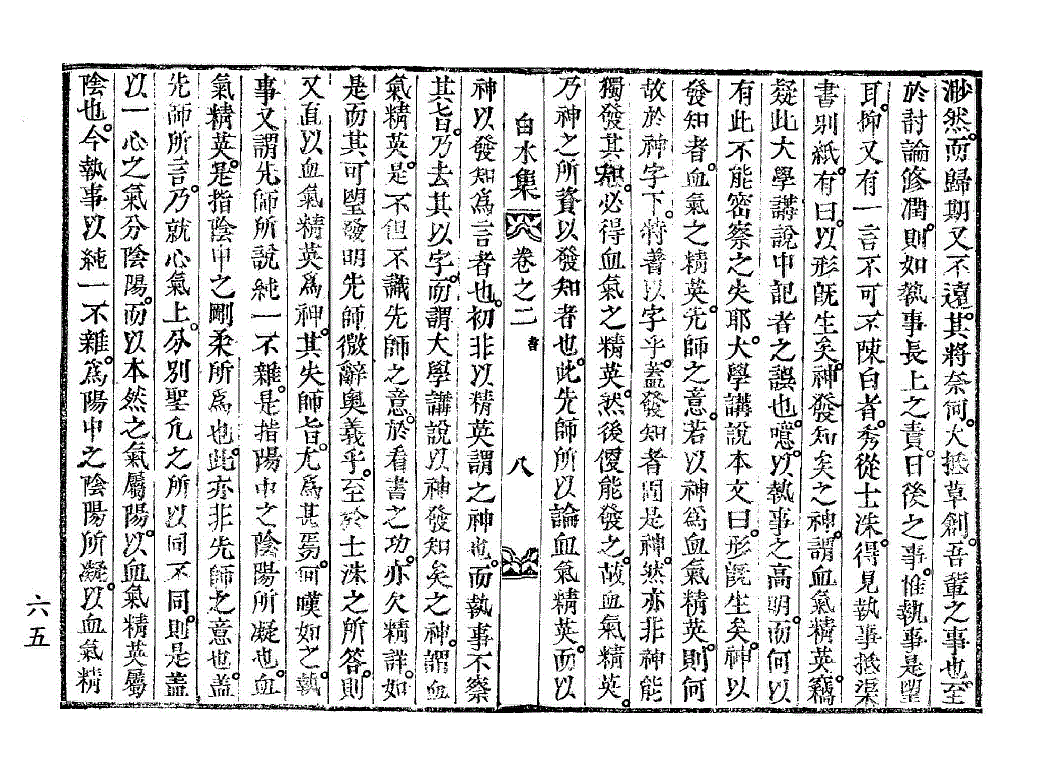 渺然。而归期又不远。其将奈何。大抵草创。吾辈之事也。至于讨论修润。则如执事长上之责。日后之事。惟执事是望耳。抑又有一言不可不陈白者。秀从士洙。得见执事抵渠书别纸。有曰。以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神。谓血气精英。窃疑此大学讲说中记者之误也。噫。以执事之高明。而何以有此不能密察之失耶。大学讲说本文曰。形既生矣。神以发知者。血气之精英。先师之意。若以神为血气精英。则何故于神字下。特着以字乎。盖发知者固是神。然亦非神能独发其知。必得血气之精英。然后便能发之。故血气精英。乃神之所资以发知者也。此先师所以论血气精英。而以神以发知为言者也。初非以精英谓之神也。而执事不察其旨。乃去其以字。而谓大学讲说以神发知矣之神。谓血气精英。是不但不识先师之意。于看书之功。亦欠精详。如是而其可望发明先师微辞奥义乎。至于士洙之所答。则又直以血气精英为神。其失师旨。尤为甚焉。何叹如之。执事又谓先师所说纯一不杂。是指阳中之阴阳所凝也。血气精英。是指阴中之刚柔所为也。此亦非先师之意也。盖先师所言。乃就心气上。分别圣凡之所以同不同。则是盖以一心之气分阴阳。而以本然之气属阳。以血气精英属阴也。今执事以纯一不杂。为阳中之阴阳所凝。以血气精
渺然。而归期又不远。其将奈何。大抵草创。吾辈之事也。至于讨论修润。则如执事长上之责。日后之事。惟执事是望耳。抑又有一言不可不陈白者。秀从士洙。得见执事抵渠书别纸。有曰。以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之神。谓血气精英。窃疑此大学讲说中记者之误也。噫。以执事之高明。而何以有此不能密察之失耶。大学讲说本文曰。形既生矣。神以发知者。血气之精英。先师之意。若以神为血气精英。则何故于神字下。特着以字乎。盖发知者固是神。然亦非神能独发其知。必得血气之精英。然后便能发之。故血气精英。乃神之所资以发知者也。此先师所以论血气精英。而以神以发知为言者也。初非以精英谓之神也。而执事不察其旨。乃去其以字。而谓大学讲说以神发知矣之神。谓血气精英。是不但不识先师之意。于看书之功。亦欠精详。如是而其可望发明先师微辞奥义乎。至于士洙之所答。则又直以血气精英为神。其失师旨。尤为甚焉。何叹如之。执事又谓先师所说纯一不杂。是指阳中之阴阳所凝也。血气精英。是指阴中之刚柔所为也。此亦非先师之意也。盖先师所言。乃就心气上。分别圣凡之所以同不同。则是盖以一心之气分阴阳。而以本然之气属阳。以血气精英属阴也。今执事以纯一不杂。为阳中之阴阳所凝。以血气精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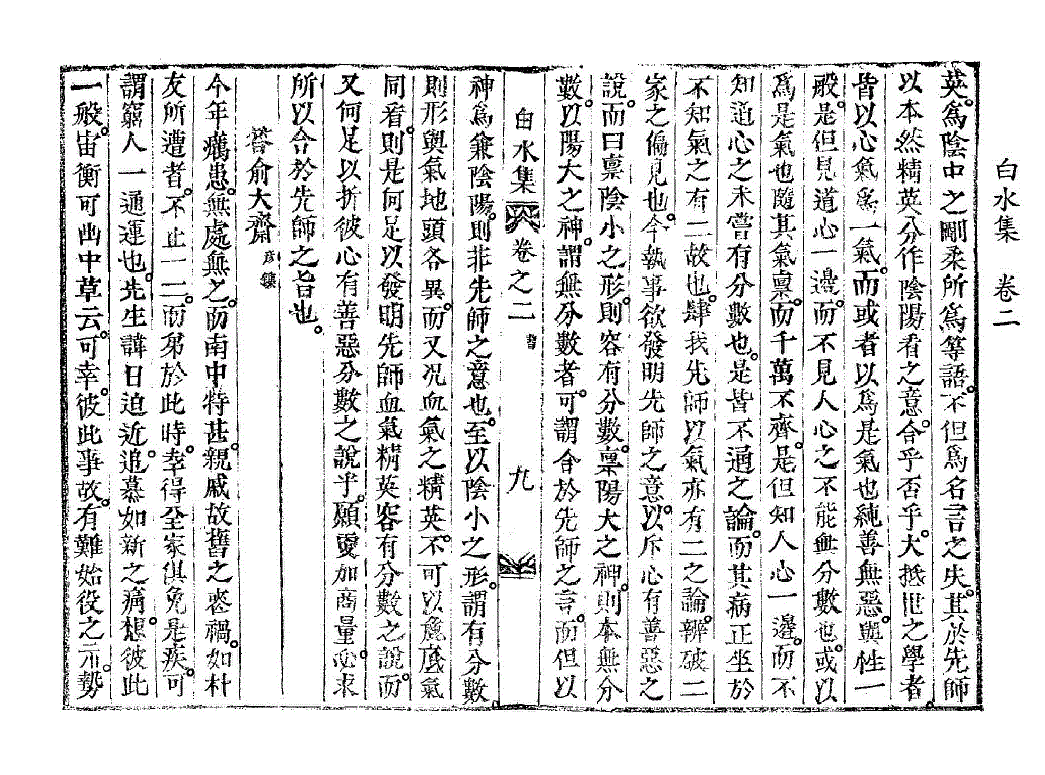 英。为阴中之刚柔所为等语。不但为名言之失。其于先师以本然精英分作阴阳看之意。合乎否乎。大抵世之学者。皆以心气为一气。而或者以为是气也纯善无恶。与性一般。是但见道心一边。而不见人心之不能无分数也。或以为是气也随其气禀。而千万不齐。是但知人心一边。而不知道心之未尝有分数也。是皆不通之论。而其病正坐于不知气之有二故也。肆我先师以气亦有二之论。辨破二家之偏见也。今执事欲发明先师之意。以斥心有善恶之说。而曰禀阴小之形。则容有分数。禀阳大之神。则本无分数。以阳大之神。谓无分数者。可谓合于先师之言。而但以神为兼阴阳。则非先师之意也。至以阴小之形。谓有分数。则形与气地头各异。而又况血气之精英。不可以粗底气同看。则是何足以发明先师血气精英容有分数之说。而又何足以折彼心有善恶分数之说乎。愿更加商量。必求所以合于先师之旨也。
英。为阴中之刚柔所为等语。不但为名言之失。其于先师以本然精英分作阴阳看之意。合乎否乎。大抵世之学者。皆以心气为一气。而或者以为是气也纯善无恶。与性一般。是但见道心一边。而不见人心之不能无分数也。或以为是气也随其气禀。而千万不齐。是但知人心一边。而不知道心之未尝有分数也。是皆不通之论。而其病正坐于不知气之有二故也。肆我先师以气亦有二之论。辨破二家之偏见也。今执事欲发明先师之意。以斥心有善恶之说。而曰禀阴小之形。则容有分数。禀阳大之神。则本无分数。以阳大之神。谓无分数者。可谓合于先师之言。而但以神为兼阴阳。则非先师之意也。至以阴小之形。谓有分数。则形与气地头各异。而又况血气之精英。不可以粗底气同看。则是何足以发明先师血气精英容有分数之说。而又何足以折彼心有善恶分数之说乎。愿更加商量。必求所以合于先师之旨也。答俞大斋(彦鏶)
今年疠患。无处无之。而南中特甚。亲戚故旧之丧祸。如朴友所遭者。不止一二。而弟于此时。幸得全家俱免是疾。可谓穷人一通运也。先生讳日迫近。追慕如新之痛。想彼此一般。宙衡可出中草云。可幸。彼此事故。有难始役之示。势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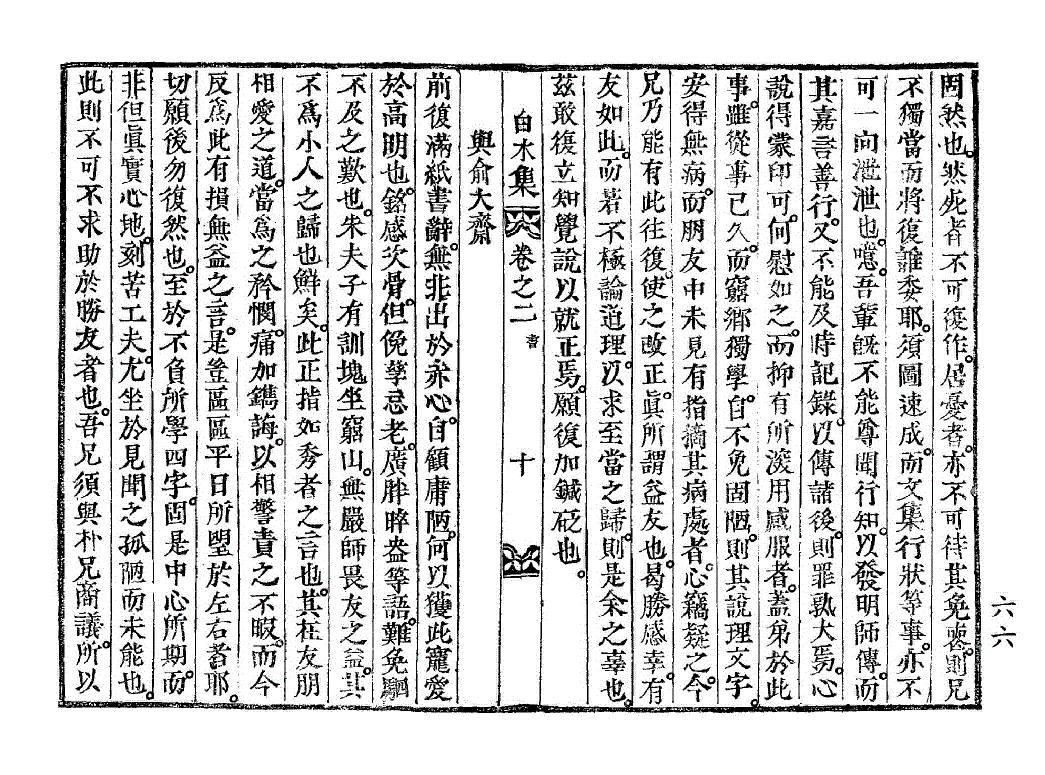 固然也。然死者不可复作。居忧者。亦不可待其免丧。则兄不独当而将复谁委耶。须图速成。而文集行状等事。亦不可一向泄泄也。噫。吾辈既不能尊闻行知。以发明师传。而其嘉言善行。又不能及时记录。以传诸后。则罪孰大焉。心说得蒙印可。何慰如之。而抑有所深用感服者。盖弟于此事。虽从事已久。而穷乡独学。自不免固陋。则其说理文字。安得无病。而朋友中未见有指摘其病处者。心窃疑之。今兄乃能有此往复。使之改正。真所谓益友也。曷胜感幸。有友如此。而若不极论道理。以求至当之归。则是余之辜也。玆敢复立知觉说以就正焉。愿复加针砭也。
固然也。然死者不可复作。居忧者。亦不可待其免丧。则兄不独当而将复谁委耶。须图速成。而文集行状等事。亦不可一向泄泄也。噫。吾辈既不能尊闻行知。以发明师传。而其嘉言善行。又不能及时记录。以传诸后。则罪孰大焉。心说得蒙印可。何慰如之。而抑有所深用感服者。盖弟于此事。虽从事已久。而穷乡独学。自不免固陋。则其说理文字。安得无病。而朋友中未见有指摘其病处者。心窃疑之。今兄乃能有此往复。使之改正。真所谓益友也。曷胜感幸。有友如此。而若不极论道理。以求至当之归。则是余之辜也。玆敢复立知觉说以就正焉。愿复加针砭也。与俞大斋
前复满纸书辞。无非出于赤心。自顾庸陋。何以获此宠爱于高明也。铭感次骨。但俛孳忘老。广胖晬盎等语。难免驷不及之叹也。朱夫子有训块坐穷山。无严师畏友之益。其不为小人之归也鲜矣。此正指如秀者之言也。其在友朋相爱之道。当为之矜悯。痛加镌诲。以相警责之不暇。而今反为此有损无益之言。是岂区区平日所望于左右者耶。切愿后勿复然也。至于不负所学四字。固是中心所期。而非但真实心地。刻苦工夫。尤坐于见闻之孤陋而未能也。此则不可不求助于胜友者也。吾兄须与朴兄商议。所以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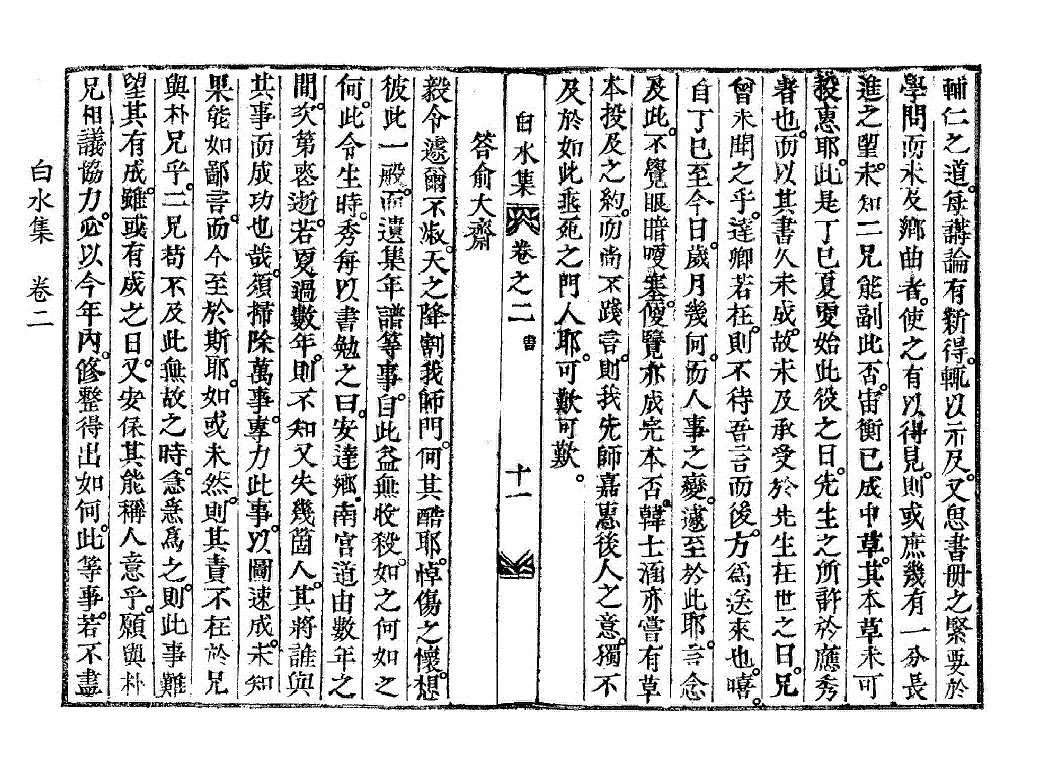 辅仁之道。每讲论有新得。辄以示及。又思书册之紧要于学问而未及乡曲者。使之有以得见。则或庶几有一分长进之望。未知二兄能副此否。宙衡已成中草。其本草未可投惠耶。此是丁巳夏更始此役之日。先生之所许于应秀者也。而以其书久未成。故未及承受于先生在世之日。兄曾未闻之乎。达卿若在。则不待吾言而后。方为送来也。嘻。自丁巳至今日。岁月几何。而人事之变。遽至于此耶。言念及此。不觉眼暗哽塞。便览亦成完本否。韩士涵亦尝有草本投及之约。而尚不践言。则我先师嘉惠后人之意。独不及于如此垂死之门人耶。可叹可叹。
辅仁之道。每讲论有新得。辄以示及。又思书册之紧要于学问而未及乡曲者。使之有以得见。则或庶几有一分长进之望。未知二兄能副此否。宙衡已成中草。其本草未可投惠耶。此是丁巳夏更始此役之日。先生之所许于应秀者也。而以其书久未成。故未及承受于先生在世之日。兄曾未闻之乎。达卿若在。则不待吾言而后。方为送来也。嘻。自丁巳至今日。岁月几何。而人事之变。遽至于此耶。言念及此。不觉眼暗哽塞。便览亦成完本否。韩士涵亦尝有草本投及之约。而尚不践言。则我先师嘉惠后人之意。独不及于如此垂死之门人耶。可叹可叹。答俞大斋
毅令遽尔不淑。天之降割我师门。何其酷耶。悼伤之怀。想彼此一般。而遗集年谱等事。自此益无收杀。如之何如之何。此令生时。秀每以书勉之曰。安达乡,南宫道由数年之间。次第丧逝。若更过数年。则不知又失几个人。其将谁与共事而成功也哉。须扫除万事。专力此事。以图速成。未知果能如鄙言。而今至于斯耶。如或未然。则其责不在于兄与朴兄乎。二兄苟不及此无故之时。急急为之。则此事难望其有成。虽或有成之日。又安保其能称人意乎。愿与朴兄相议协力。必以今年内。修整得出如何。此等事。若不尽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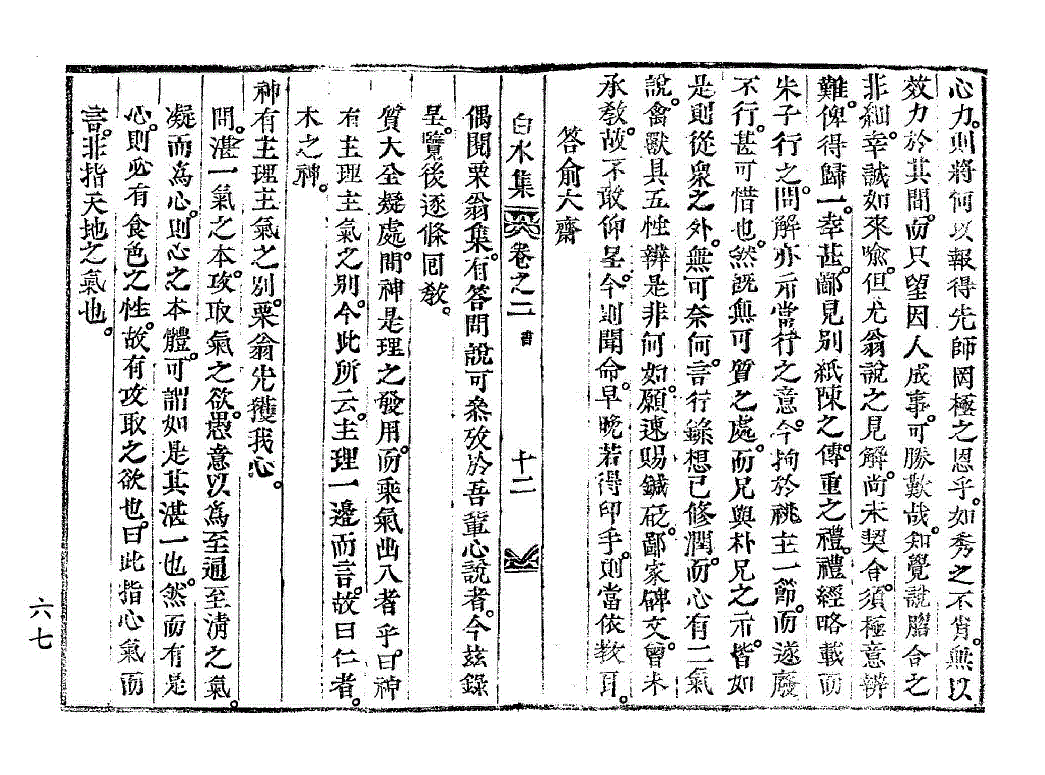 心力。则将何以报得先师罔极之恩乎。如秀之不肖。无以效力于其间。而只望因人成事。可胜叹哉。知觉说吻合之非细。幸诚如来喻。但尤翁说之见解。尚未契合。须极意辨难。俾得归一。幸甚。鄙见别纸陈之。传重之礼。礼经略载而朱子行之。问解亦示当行之意。今拘于祧主一节。而遂废不行。甚可惜也。然既无可质之处。而兄与朴兄之示。皆如是则从众之外。无可奈何。言行录想已修润。而心有二气说。禽兽具五性辨是非何如。愿速赐针砭。鄙家碑文。曾未承教。故不敢仰呈。今则闻命。早晚若得印手。则当依教耳。
心力。则将何以报得先师罔极之恩乎。如秀之不肖。无以效力于其间。而只望因人成事。可胜叹哉。知觉说吻合之非细。幸诚如来喻。但尤翁说之见解。尚未契合。须极意辨难。俾得归一。幸甚。鄙见别纸陈之。传重之礼。礼经略载而朱子行之。问解亦示当行之意。今拘于祧主一节。而遂废不行。甚可惜也。然既无可质之处。而兄与朴兄之示。皆如是则从众之外。无可奈何。言行录想已修润。而心有二气说。禽兽具五性辨是非何如。愿速赐针砭。鄙家碑文。曾未承教。故不敢仰呈。今则闻命。早晚若得印手。则当依教耳。答俞大斋
偶阅栗翁集。有答问说可参考于吾辈心说者。今玆录呈。览后逐条回教。
质大全疑处。问神是理之发用。而乘气出入者乎。曰神有主理主气之别。今此所云。主理一边而言。故曰仁者。木之神。
神有主理主气之别。栗翁先获我心。
问。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愚意以为至通至清之气。凝而为心。则心之本体。可谓如是其湛一也。然而有是心。则必有食色之性。故有攻取之欲也。曰此指心气而言。非指天地之气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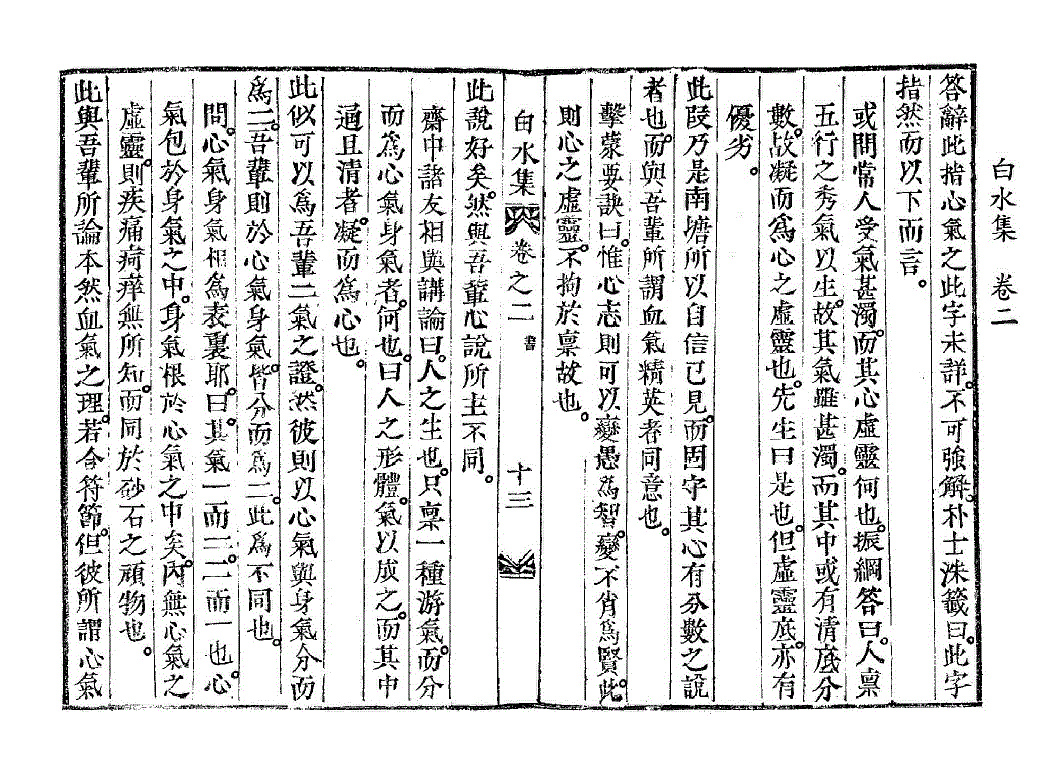 答辞此指心气之此字未详。不可强解。朴士洙签曰。此字指然而以下而言。
答辞此指心气之此字未详。不可强解。朴士洙签曰。此字指然而以下而言。或问常人受气甚浊。而其心虚灵何也。振纲答曰。人禀五行之秀气以生。故其气虽甚浊。而其中或有清底分数。故凝而为心之虚灵也。先生曰是也。但虚灵底。亦有优劣。
此段乃是南塘所以自信己见。而固守其心有分数之说者也。而与吾辈所谓血气精英者同意也。
击蒙要诀曰。惟心志则可以变愚为智。变不肖为贤。此则心之虚灵。不拘于禀故也。
此说好矣。然与吾辈心说所主不同。
斋中诸友相与讲论曰。人之生也。只禀一种游气。而分而为心气身气者。何也。曰人之形体。气以成之。而其中通且清者。凝而为心也。
此似可以为吾辈二气之證。然彼则以心气与身气分而为二。吾辈则于心气身气。皆分而为二。此为不同也。
问。心气身气相为表里耶。曰。其气一而二。二而一也。心气包于身气之中。身气根于心气之中矣。内无心气之虚灵。则疾痛疴痒无所知。而同于砂石之顽物也。
此与吾辈所论本然血气之理。若合符节。但彼所谓心气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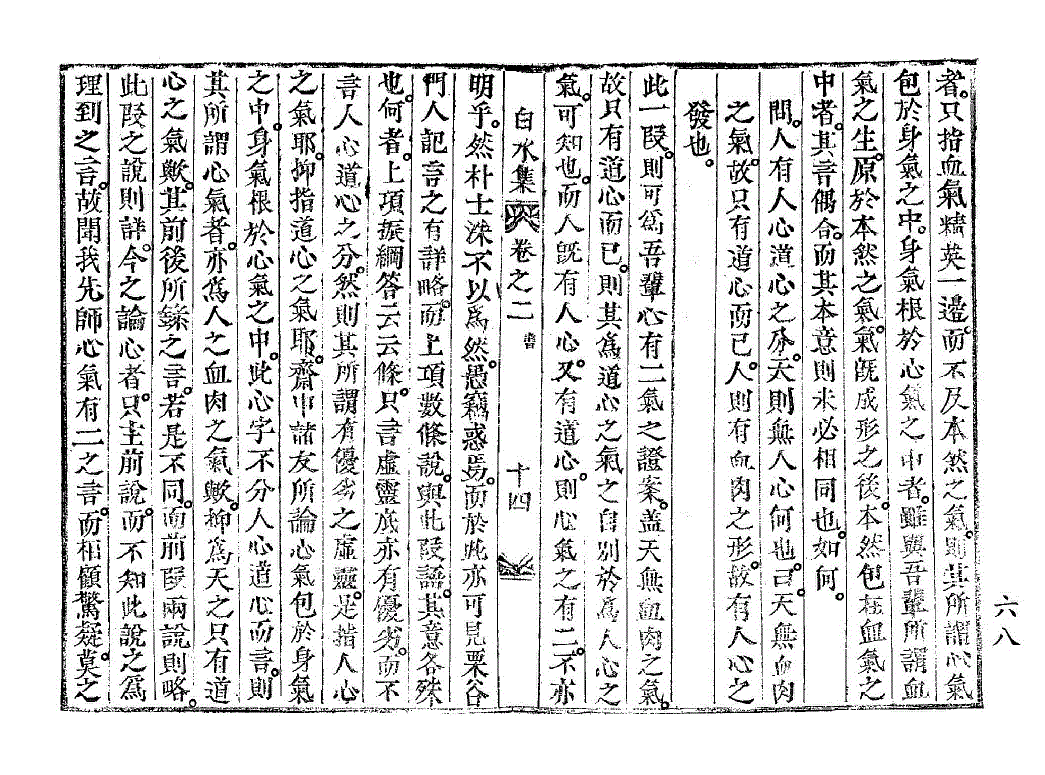 者。只指血气精英一边。而不及本然之气。则其所谓心气包于身气之中。身气根于心气之中者。虽与吾辈所谓血气之生。原于本然之气。气既成形之后。本然包在血气之中者。其言偶合。而其本意则未必相同也。如何。
者。只指血气精英一边。而不及本然之气。则其所谓心气包于身气之中。身气根于心气之中者。虽与吾辈所谓血气之生。原于本然之气。气既成形之后。本然包在血气之中者。其言偶合。而其本意则未必相同也。如何。问。人有人心道心之分。天则无人心何也。曰。天无血肉之气。故只有道心而已。人则有血肉之形。故有人心之发也。
此一段。则可为吾辈心有二气之證案。盖天无血肉之气。故只有道心而已。则其为道心之气之自别于为人心之气。可知也。而人既有人心。又有道心。则心气之有二。不亦明乎。然朴士洙不以为然。愚窃惑焉。而于此亦可见栗谷门人记言之有详略。而上项数条说。与此段语。其意各殊也。何者。上项振纲答云云条。只言虚灵底亦有优劣。而不言人心道心之分。然则其所谓有优劣之虚灵。是指人心之气耶。抑指道心之气耶。斋中诸友所论心气包于身气之中。身气根于心气之中。此心字不分人心道心而言。则其所谓心气者。亦为人之血肉之气欤。抑为天之只有道心之气欤。其前后所录之言。若是不同。而前段两说则略。此段之说则详。今之论心者。只主前说。而不知此说之为理到之言。故闻我先师心气有二之言。而相顾惊疑。莫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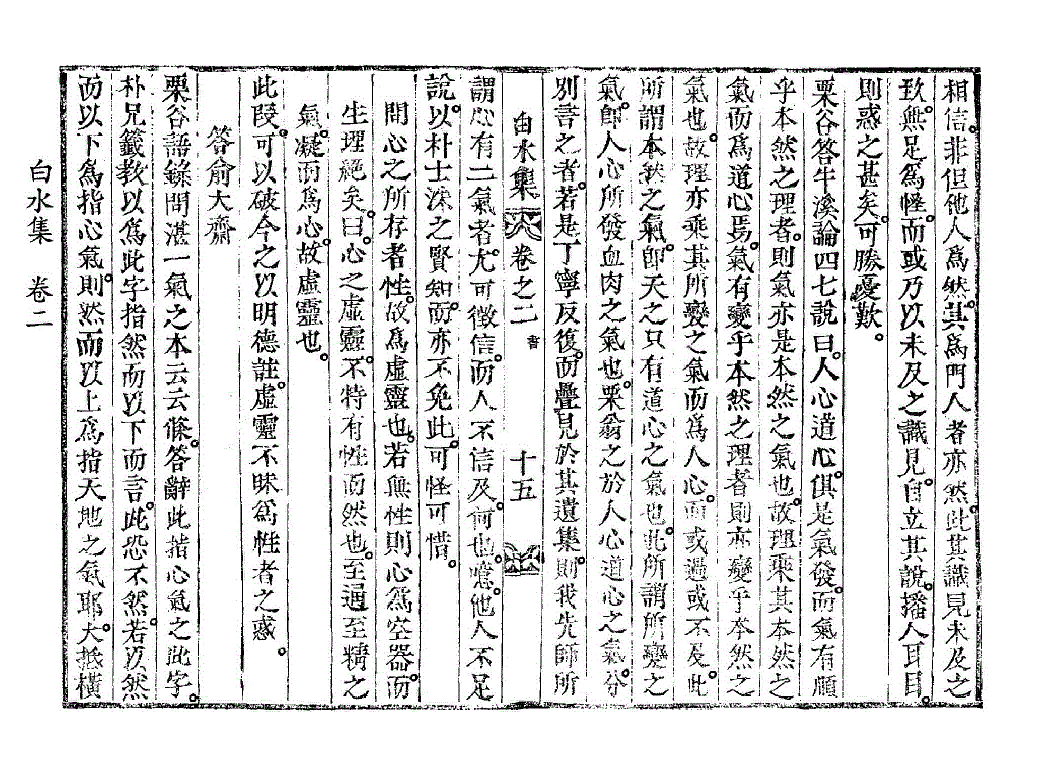 相信。非但他人为然。其为门人者亦然。此其识见未及之致。无足为怪。而或乃以未及之识见。自立其说。播人耳目。则惑之甚矣。可胜忧叹。
相信。非但他人为然。其为门人者亦然。此其识见未及之致。无足为怪。而或乃以未及之识见。自立其说。播人耳目。则惑之甚矣。可胜忧叹。栗谷答牛溪论四七说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亦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此所谓本然之气。即天之只有道心之气也。此所谓所变之气。即人心所发血肉之气也。栗翁之于人心道心之气。分别言之者。若是丁宁反复。而叠见于其遗集。则我先师所谓心有二气者。尤可徵信。而人不信及。何也。噫。他人不足说。以朴士洙之贤知。而亦不免此。可怪可惜。
问。心之所存者性。故为虚灵也。若无性则心为空器。而生理绝矣。曰。心之虚灵。不特有性而然也。至通至精之气。凝而为心。故虚灵也。
此段。可以破今之以明德注。虚灵不昧为性者之惑。
答俞大斋
栗谷语录问湛一气之本云云条。答辞此指心气之此字。朴兄签教以为此字指然而以下而言。此恐不然。若以然而以下为指心气。则然而以上为指天地之气耶。大抵横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6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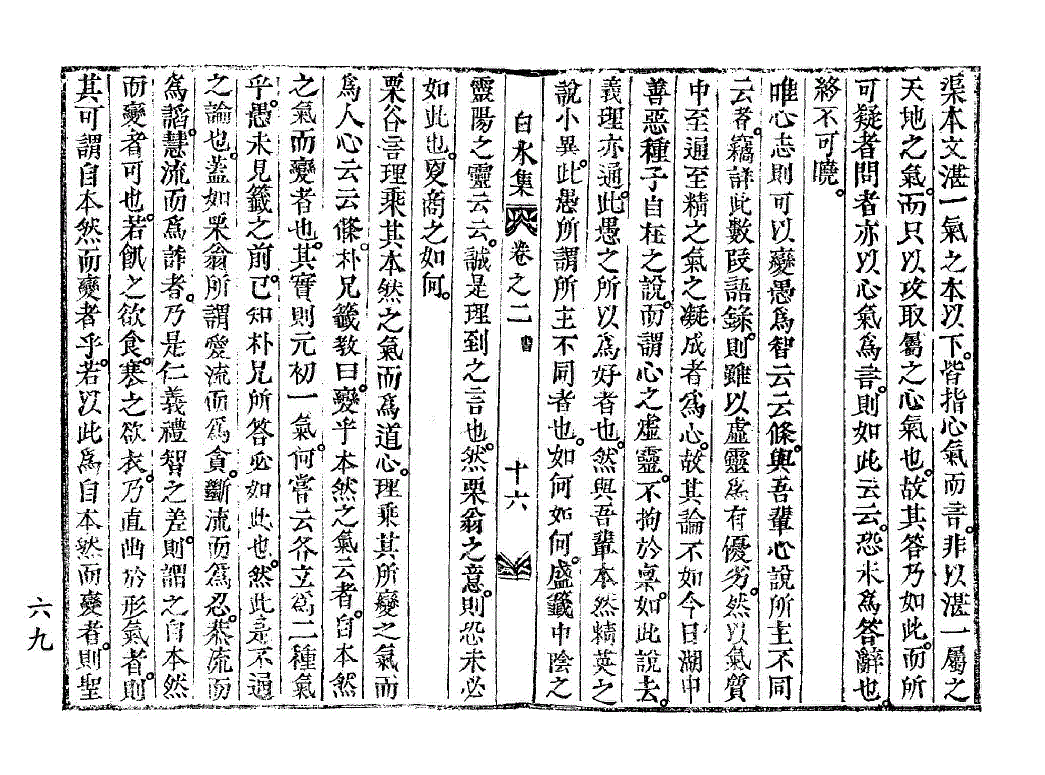 渠本文湛一气之本以下。皆指心气而言。非以湛一属之天地之气。而只以攻取属之心气也。故其答乃如此。而所可疑者问者亦以心气为言。则如此云云。恐未为答辞也。终不可晓。
渠本文湛一气之本以下。皆指心气而言。非以湛一属之天地之气。而只以攻取属之心气也。故其答乃如此。而所可疑者问者亦以心气为言。则如此云云。恐未为答辞也。终不可晓。唯心志则可以变愚为智云云条。与吾辈心说所主不同云者。窃详此数段语录。则虽以虚灵为有优劣。然以气质中至通至精之气之凝成者为心。故其论不如今日湖中善恶种子自在之说。而谓心之虚灵。不拘于禀。如此说去。义理亦通。此愚之所以为好者也。然与吾辈本然精英之说小异。此愚所谓所主不同者也。如何如何。盛签中阴之灵阳之灵云云。诚是理到之言也。然栗翁之意。则恐未必如此也。更商之如何。
栗谷言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理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云云条。朴兄签教曰。变乎本然之气云者。自本然之气而变者也。其实则元初一气。何尝云各立为二种气乎。愚未见签之前。已知朴兄所答必如此也。然此是不通之论也。盖如栗翁所谓爱流而为贪。断流而为忍。恭流而为谄。慧流而为诈者。乃是仁义礼智之差。则谓之自本然而变者可也。若饥之欲食。寒之欲衣。乃直出于形气者。则其可谓自本然而变者乎。若以此为自本然而变者。则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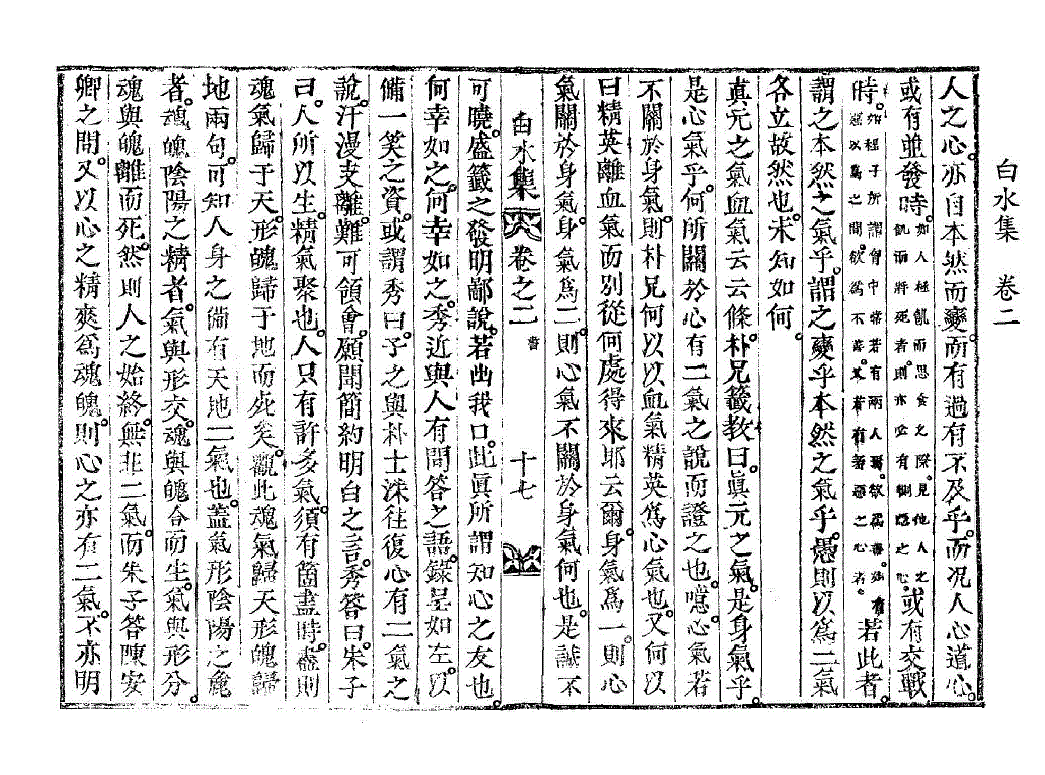 人之心。亦自本然而变。而有过有不及乎。而况人心道心。或有并发时。(如人极饥而思食之际。见他人之饥而将死者。则亦必有恻隐之心。)或有交战时。(如程子所谓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若此者。谓之本然之气乎。谓之变乎本然之气乎。愚则以为二气各立故然也。未知如何。
人之心。亦自本然而变。而有过有不及乎。而况人心道心。或有并发时。(如人极饥而思食之际。见他人之饥而将死者。则亦必有恻隐之心。)或有交战时。(如程子所谓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若此者。谓之本然之气乎。谓之变乎本然之气乎。愚则以为二气各立故然也。未知如何。真元之气血气云云条。朴兄签教曰。真元之气。是身气乎。是心气乎。何所关于心有二气之说而證之也。噫。心气若不关于身气。则朴兄何以以血气精英为心气也。又何以曰精英离血气而别从何处得来耶云尔。身气为一。则心气关于身气。身气为二。则心气不关于身气何也。是诚不可晓。盛签之发明鄙说。若出我口。此真所谓知心之友也。何幸如之。何幸如之。秀近与人有问答之语。录呈如左。以备一笑之资。或谓秀曰。子之与朴士洙往复心有二气之说。汗漫支离。难可领会。愿闻简约明白之言。秀答曰。朱子曰。人所以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观此魂气归天形魄归地两句。可知人身之备有天地二气也。盖气形阴阳之粗者。魂魄阴阳之精者。气与形交。魂与魄合而生。气与形分。魂与魄离而死。然则人之始终。无非二气。而朱子答陈安卿之问。又以心之精爽为魂魄。则心之亦有二气。不亦明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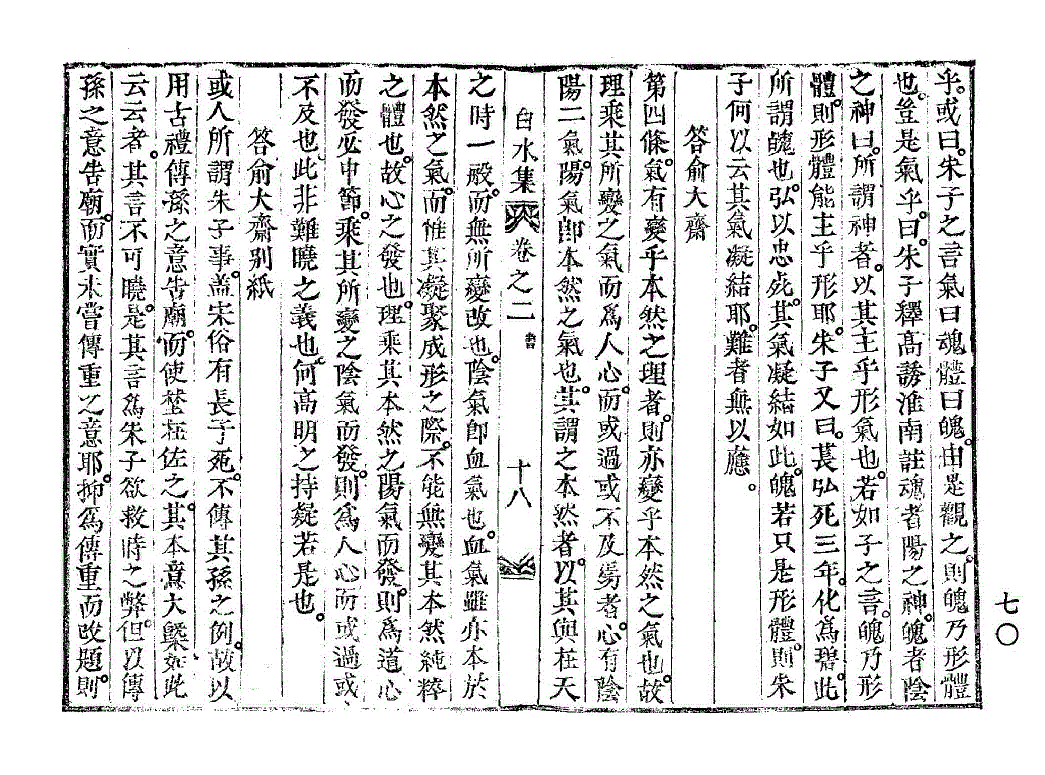 乎。或曰。朱子之言气曰魂体曰魄。由是观之。则魄乃形体也。岂是气乎。曰。朱子释高诱淮南注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曰。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若如子之言。魄乃形体。则形体能主乎形耶。朱子又曰。苌弘死三年。化为碧。此所谓魄也。弘以忠死。其气凝结如此。魄若只是形体。则朱子何以云其气凝结耶。难者无以应。
乎。或曰。朱子之言气曰魂体曰魄。由是观之。则魄乃形体也。岂是气乎。曰。朱子释高诱淮南注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曰。所谓神者。以其主乎形气也。若如子之言。魄乃形体。则形体能主乎形耶。朱子又曰。苌弘死三年。化为碧。此所谓魄也。弘以忠死。其气凝结如此。魄若只是形体。则朱子何以云其气凝结耶。难者无以应。答俞大斋
第四条。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焉者。心有阴阳二气。阳气即本然之气也。其谓之本然者。以其与在天之时一般。而无所变改也。阴气即血气也。血气虽亦本于本然之气。而惟其凝聚成形之际。不能无变其本然纯粹之体也。故心之发也。理乘其本然之阳气而发。则为道心而发必中节。乘其所变之阴气而发。则为人心而或过或不及也。此非难晓之义也。何高明之持疑若是也。
答俞大斋别纸
或人所谓朱子事。盖宋俗有长子死。不传其孙之例。故以用古礼传孙之意告庙。而使野在佐之。其本意大槩如此云云者。其言不可晓。是其言为朱子欲救时之弊。但以传孙之意告庙。而实未尝传重之意耶。抑为传重而改题。则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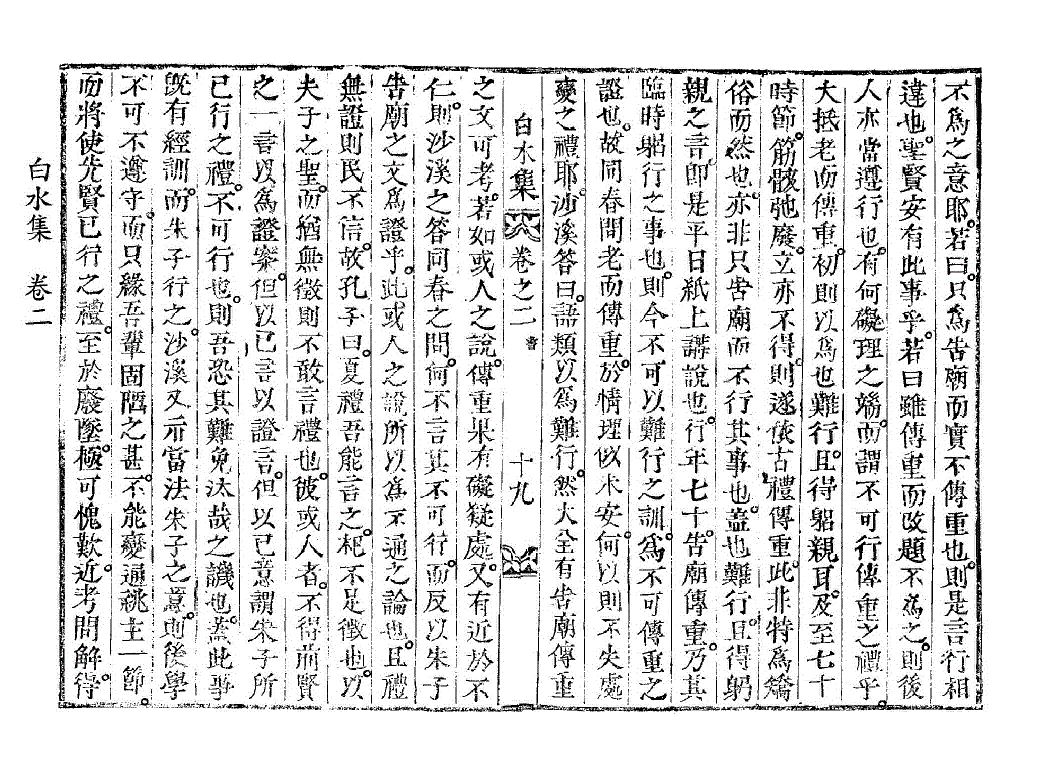 不为之意耶。若曰。只为告庙而实不传重也。则是言行相违也。圣贤安有此事乎。若曰虽传重而改题不为之。则后人亦当遵行也。有何碍理之端。而谓不可行传重之礼乎。大抵老而传重。初则以为也难行。且得躬亲耳。及至七十时节。筋骸弛废。立亦不得。则遂依古礼传重。此非特为矫俗而然也。亦非只告庙而不行其事也。盖也难行。且得躬亲之言。即是平日纸上讲说也。行年七十。告庙传重。乃其临时躬行之事也。则今不可以难行之训。为不可传重之證也。故同春问老而传重。于情理似未安。何以则不失处变之礼耶。沙溪答曰。语类以为难行。然大全有告庙传重之文可考。若如或人之说。传重果有碍疑处。又有近于不仁。则沙溪之答同春之问。何不言其不可行。而反以朱子告庙之文为證乎。此或人之说所以为不通之论也。且礼无證则民不信。故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以夫子之圣。而犹无徵则不敢言礼也。彼或人者。不得前贤之一言以为證案。但以己言以證言。但以己意谓朱子所已行之礼。不可行也。则吾恐其难免汰哉之讥也。盖此事既有经训。而朱子行之。沙溪又示当法朱子之意。则后学不可不遵守。而只缘吾辈固陋之甚。不能变通祧主一节。而将使先贤已行之礼。至于废坠。极可愧叹。近考问解。得
不为之意耶。若曰。只为告庙而实不传重也。则是言行相违也。圣贤安有此事乎。若曰虽传重而改题不为之。则后人亦当遵行也。有何碍理之端。而谓不可行传重之礼乎。大抵老而传重。初则以为也难行。且得躬亲耳。及至七十时节。筋骸弛废。立亦不得。则遂依古礼传重。此非特为矫俗而然也。亦非只告庙而不行其事也。盖也难行。且得躬亲之言。即是平日纸上讲说也。行年七十。告庙传重。乃其临时躬行之事也。则今不可以难行之训。为不可传重之證也。故同春问老而传重。于情理似未安。何以则不失处变之礼耶。沙溪答曰。语类以为难行。然大全有告庙传重之文可考。若如或人之说。传重果有碍疑处。又有近于不仁。则沙溪之答同春之问。何不言其不可行。而反以朱子告庙之文为證乎。此或人之说所以为不通之论也。且礼无證则民不信。故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以夫子之圣。而犹无徵则不敢言礼也。彼或人者。不得前贤之一言以为證案。但以己言以證言。但以己意谓朱子所已行之礼。不可行也。则吾恐其难免汰哉之讥也。盖此事既有经训。而朱子行之。沙溪又示当法朱子之意。则后学不可不遵守。而只缘吾辈固陋之甚。不能变通祧主一节。而将使先贤已行之礼。至于废坠。极可愧叹。近考问解。得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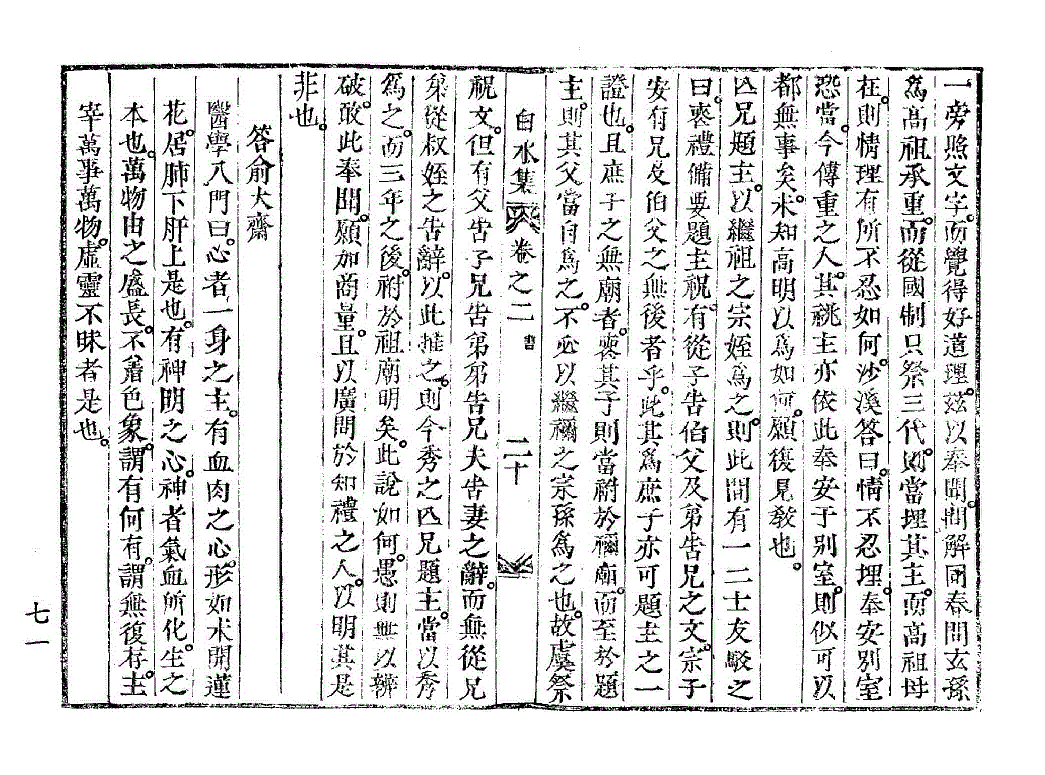 一旁照文字。而觉得好道理。玆以奉闻。问解同春问玄孙为高祖承重。而从国制只祭三代。则当埋其主。而高祖母在。则情理有所不忍如何。沙溪答曰。情不忍埋。奉安别室恐当。今传重之人。其祧主亦依此奉安于别室。则似可以都无事矣。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愿复见教也。
一旁照文字。而觉得好道理。玆以奉闻。问解同春问玄孙为高祖承重。而从国制只祭三代。则当埋其主。而高祖母在。则情理有所不忍如何。沙溪答曰。情不忍埋。奉安别室恐当。今传重之人。其祧主亦依此奉安于别室。则似可以都无事矣。未知高明以为如何。愿复见教也。亡兄题主。以继祖之宗侄为之。则此间有一二士友驳之曰。丧礼备要题主祝。有从子告伯父及弟告兄之文。宗子安有兄及伯父之无后者乎。此其为庶子亦可题主之一證也。且庶子之无庙者。丧其子则当祔于祢庙。而至于题主。则其父当自为之。不必以继祢之宗孙为之也。故虞祭祝文。但有父告子兄告弟弟告兄夫告妻之辞。而无从兄弟从叔侄之告辞。以此推之。则今秀之亡兄题主。当以秀为之。而三年之后。祔于祖庙明矣。此说如何。愚则无以辨破。敢此奉闻。愿加商量。且以广问于知礼之人。以明其是非也。
答俞大斋
医学入门曰。心者。一身之主。有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居肺下肝上是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不着色象。谓有何有。谓无复存。主宰万事万物。虚灵不昧者是也。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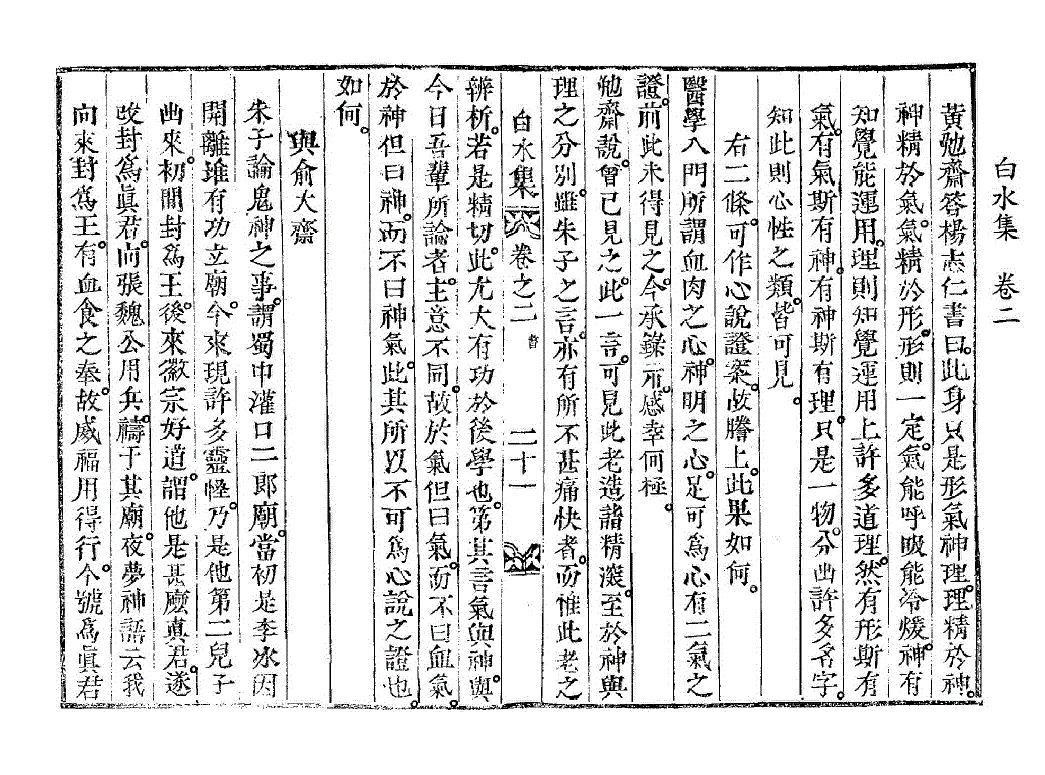 黄勉斋答杨志仁书曰。此身只是形气神理。理精于神。神精于气。气精于形。形则一定。气能呼吸能冷煖。神有知觉能运用。理则知觉运用上许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气。有气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许多名字。知此则心性之类。皆可见。
黄勉斋答杨志仁书曰。此身只是形气神理。理精于神。神精于气。气精于形。形则一定。气能呼吸能冷煖。神有知觉能运用。理则知觉运用上许多道理。然有形斯有气。有气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许多名字。知此则心性之类。皆可见。右二条。可作心说證案。故誊上。此果如何。
医学入门所谓血肉之心。神明之心。足可为心有二气之證。前此未得见之。今承录示。感幸何极。
勉斋说。曾已见之。此一言。可见此老造诣精深。至于神与理之分别。虽朱子之言。亦有所不甚痛快者。而惟此老之辨析。若是精切。此尤大有功于后学也。第其言气与神。与今日吾辈所论者。主意不同。故于气但曰气。而不曰血气。于神但曰神。而不曰神气。此其所以不可为心说之證也。如何。
与俞大斋
朱子论鬼神之事。谓蜀中灌口二郎庙。当初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谓他是甚么真君。遂改封为真君。向张魏公用兵。祷于其庙。夜梦神语云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号为真君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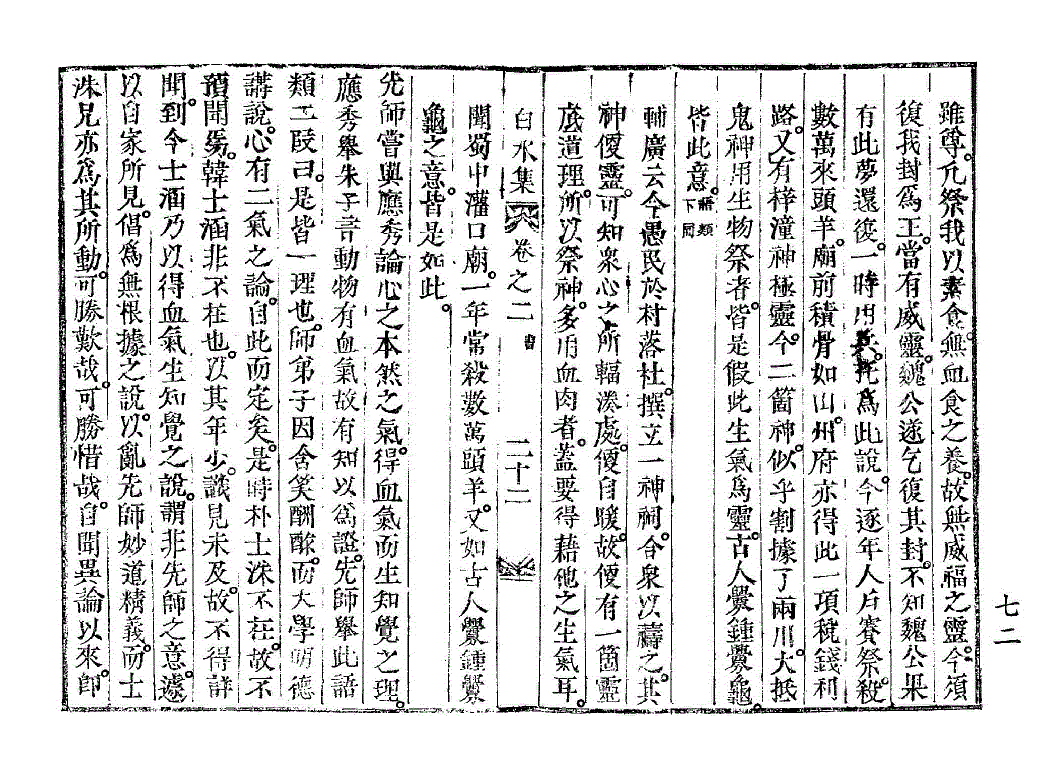 虽尊。凡祭我以素食。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我封为王。当有威灵。魏公遂乞复其封。不知魏公果有此梦还复。一时用兵。托为此说。今逐年人户赛祭。杀数万来头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项税钱利路。又有梓潼神极灵。今二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语类下同)
虽尊。凡祭我以素食。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我封为王。当有威灵。魏公遂乞复其封。不知魏公果有此梦还复。一时用兵。托为此说。今逐年人户赛祭。杀数万来头羊。庙前积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项税钱利路。又有梓潼神极灵。今二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语类下同)辅广云今愚民于村落社。撰立一神祠。合众以祷之。其神便灵。可知众心之所辐凑处。便自暖。故便有一个灵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盖要得藉他之生气耳。闻蜀中灌口庙。一年常杀数万头羊。又如古人衅钟衅龟之意。皆是如此。
先师尝与应秀论心之本然之气。得血气而生知觉之理。应秀举朱子言动物有血气故有知以为證。先师举此语类二段曰。是皆一理也。师弟子因含笑酬酢。而大学明德讲说。心有二气之论。自此而定矣。是时朴士洙不在。故不预闻焉。韩士涵非不在也。以其年少。识见未及。故不得详闻。到今士涵乃以得血气生知觉之说。谓非先师之意。遽以自家所见。倡为无根据之说。以乱先师妙道精义。而士洙兄亦为其所动。可胜叹哉。可胜惜哉。自闻异论以来。即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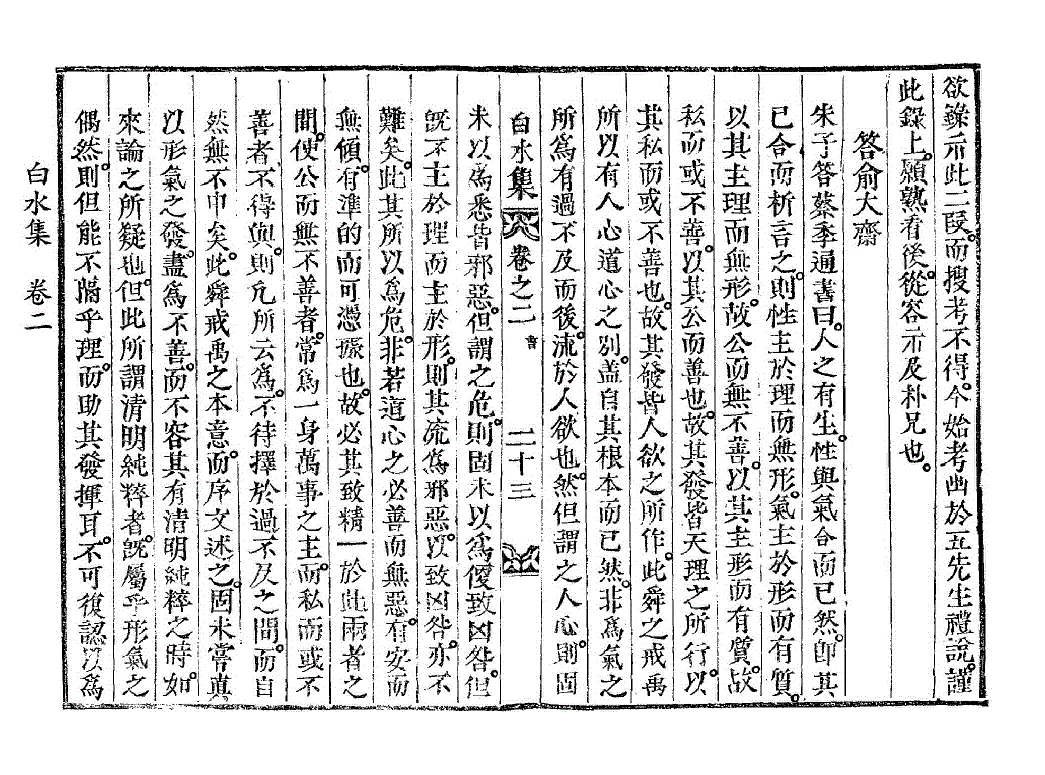 欲录示此二段。而搜考不得。今始考出于五先生礼说。谨此录上。愿熟看后。从容示及朴兄也。
欲录示此二段。而搜考不得。今始考出于五先生礼说。谨此录上。愿熟看后。从容示及朴兄也。答俞大斋
朱子答蔡季通书曰。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然但谓之人心。则固未以为悉皆邪恶。但谓之危。则固未以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则其流为邪恶。以致凶咎。亦不难矣。此其所以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无恶。有安而无倾。有准的而可凭据也。故必其致精一于此两者之间。使公而无不善者。常为一身万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与。则凡所云为。不待择于过不及之间。而自然无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真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论之所疑也。但此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耳。不可复认以为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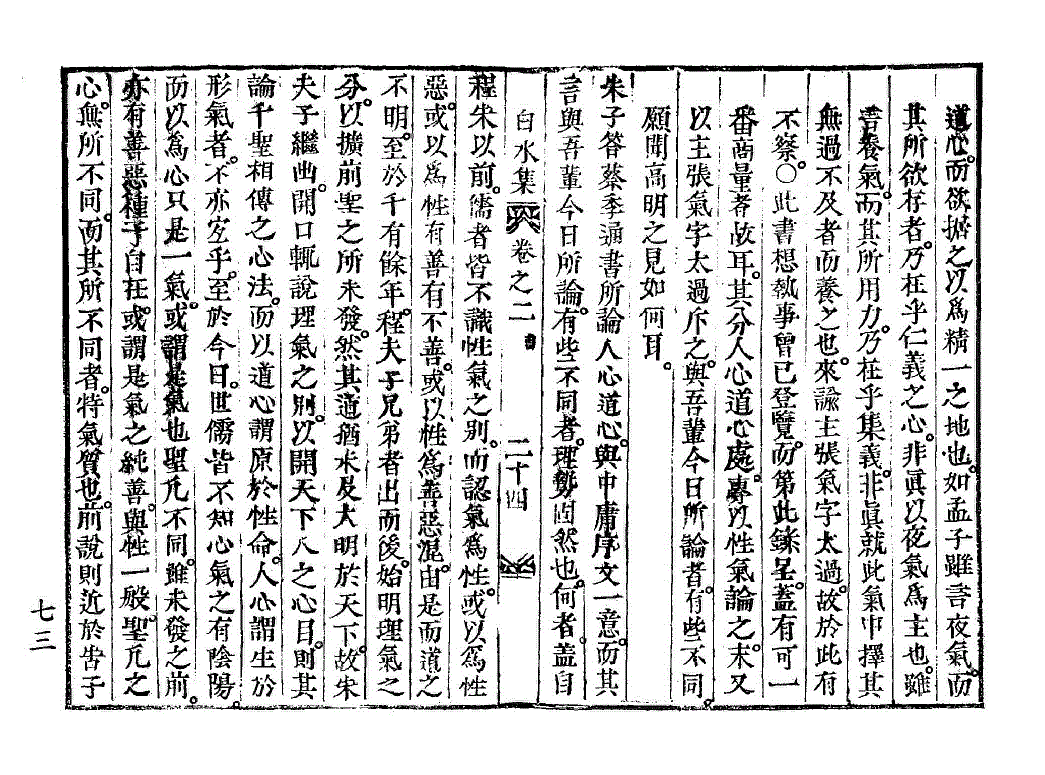 道心。而欲据之以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虽言夜气。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义之心。非真以夜气为主也。虽言养气。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义。非真就此气中择其无过不及者而养之也。来谕主张气字太过。故于此有不察。○此书想执事曾已登览。而第此录呈。盖有可一番商量者故耳。其分人心道心处。专以性气论之。末又以主张气字太过斥之。与吾辈今日所论者。有些不同。愿闻高明之见如何耳。
道心。而欲据之以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虽言夜气。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义之心。非真以夜气为主也。虽言养气。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义。非真就此气中择其无过不及者而养之也。来谕主张气字太过。故于此有不察。○此书想执事曾已登览。而第此录呈。盖有可一番商量者故耳。其分人心道心处。专以性气论之。末又以主张气字太过斥之。与吾辈今日所论者。有些不同。愿闻高明之见如何耳。朱子答蔡季通书所论人心道心。与中庸序文一意。而其言与吾辈今日所论。有些不同者。理势固然也。何者。盖自程朱以前。儒者皆不识性气之别。而认气为性。或以为性恶。或以为性有善有不善。或以性为善恶混。由是而道之不明。至于千有馀年。程夫子兄弟者出而后。始明理气之分。以扩前圣之所未发。然其道犹未及大明于天下。故朱夫子继出。开口辄说理气之别。以开天下人之心目。则其论千圣相传之心法。而以道心谓原于性命。人心谓生于形气者。不亦宜乎。至于今日。世儒皆不知心气之有阴阳。而以为心只是一气。或谓是气也圣凡不同。虽未发之前。亦有善恶种子自在。或谓是气之纯善。与性一般。圣凡之心。无所不同。而其所不同者。特气质也。前说则近于告子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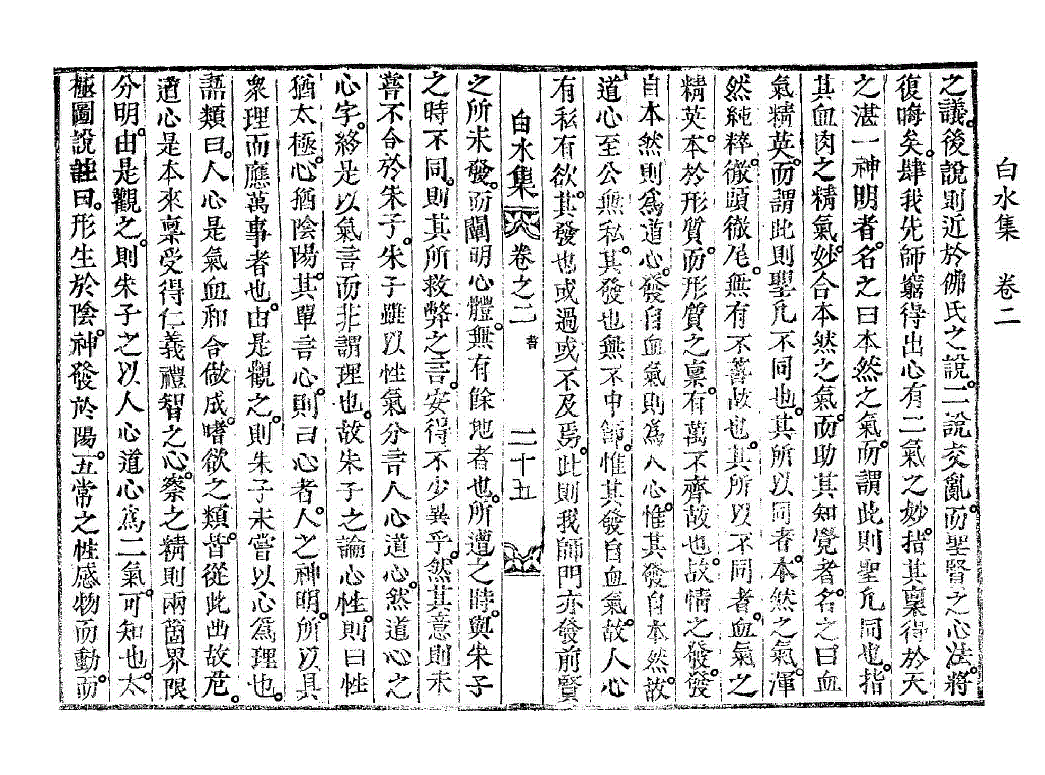 之议。后说则近于佛氏之说。二说交乱。而圣贤之心法。将复晦矣。肆我先师穷得出心有二气之妙。指其禀得于天之湛一神明者。名之曰本然之气。而谓此则圣凡同也。指其血肉之精气。妙合本然之气。而助其知觉者。名之曰血气精英。而谓此则圣凡不同也。其所以同者。本然之气。浑然纯粹。彻头彻尾。无有不善故也。其所以不同者。血气之精英。本于形质。而形质之禀。有万不齐故也。故情之发。发自本然则为道心。发自血气则为人心。惟其发自本然。故道心至公无私。其发也无不中节。惟其发自血气。故人心有私有欲。其发也或过或不及焉。此则我师门亦发前贤之所未发。而阐明心体。无有馀地者也。所遭之时。与朱子之时不同。则其所救弊之言。安得不少异乎。然其意则未尝不合于朱子。朱子虽以性气分言人心道心。然道心之心字。终是以气言而非谓理也。故朱子之论心性。则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其单言心。则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由是观之。则朱子未尝以心为理也。语类曰。人心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由是观之。则朱子之以人心道心为二气。可知也。太极图说注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
之议。后说则近于佛氏之说。二说交乱。而圣贤之心法。将复晦矣。肆我先师穷得出心有二气之妙。指其禀得于天之湛一神明者。名之曰本然之气。而谓此则圣凡同也。指其血肉之精气。妙合本然之气。而助其知觉者。名之曰血气精英。而谓此则圣凡不同也。其所以同者。本然之气。浑然纯粹。彻头彻尾。无有不善故也。其所以不同者。血气之精英。本于形质。而形质之禀。有万不齐故也。故情之发。发自本然则为道心。发自血气则为人心。惟其发自本然。故道心至公无私。其发也无不中节。惟其发自血气。故人心有私有欲。其发也或过或不及焉。此则我师门亦发前贤之所未发。而阐明心体。无有馀地者也。所遭之时。与朱子之时不同。则其所救弊之言。安得不少异乎。然其意则未尝不合于朱子。朱子虽以性气分言人心道心。然道心之心字。终是以气言而非谓理也。故朱子之论心性。则曰性犹太极。心犹阴阳。其单言心。则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由是观之。则朱子未尝以心为理也。语类曰。人心是气血和合做成。嗜欲之类。皆从此出故危。道心是本来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察之精则两个界限分明。由是观之。则朱子之以人心道心为二气。可知也。太极图说注曰。形生于阴。神发于阳。五常之性感物而动。而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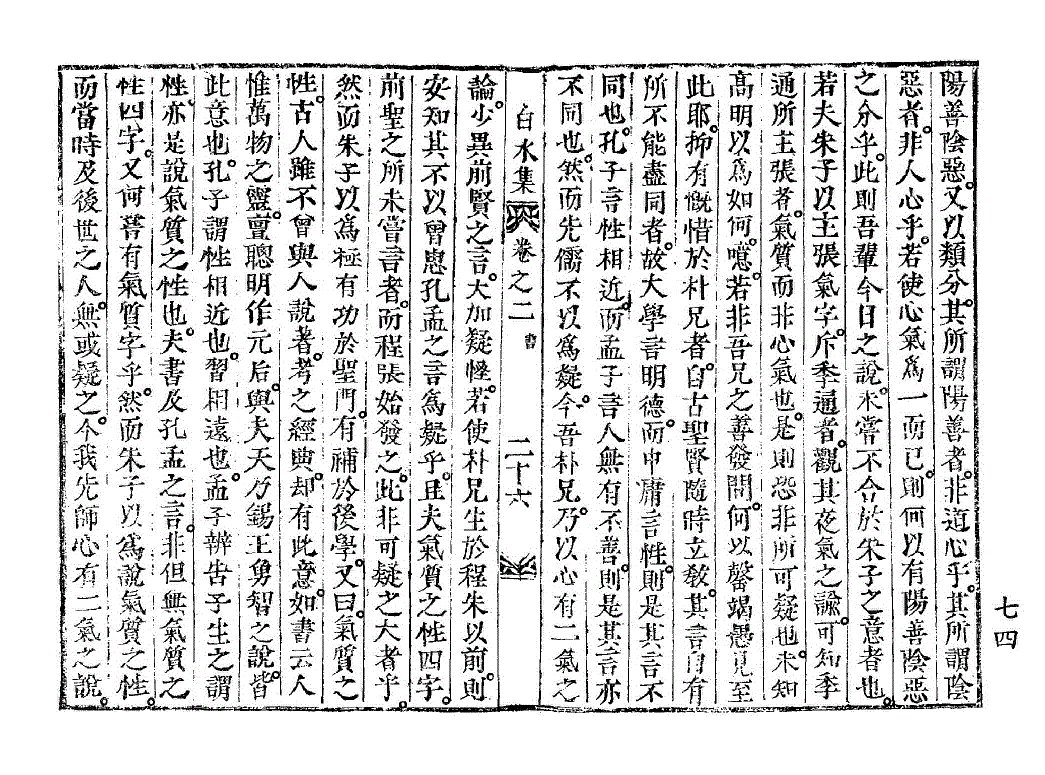 阳善阴恶。又以类分。其所谓阳善者。非道心乎。其所谓阴恶者。非人心乎。若使心气为一而已。则何以有阳善阴恶之分乎。此则吾辈今日之说。未尝不合于朱子之意者也。若夫朱子以主张气字。斥季通者。观其夜气之谕。可知季通所主张者。气质而非心气也。是则恐非所可疑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噫。若非吾兄之善发问。何以罄竭愚见至此耶。抑有慨惜于朴兄者。自古圣贤随时立教。其言自有所不能尽同者。故大学言明德。而中庸言性。则是其言不同也。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人无有不善。则是其言亦不同也。然而先儒不以为疑。今吾朴兄。乃以心有二气之论。少异前贤之言。大加疑怪。若使朴兄生于程朱以前。则安知其不以曾思孔孟之言为疑乎。且夫气质之性四字。前圣之所未尝言者。而程张始发之。此非可疑之大者乎。然而朱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又曰。气质之性。古人虽不曾与人说著。考之经典。却有此意。如书云人惟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与夫天乃锡王勇智之说。皆此意也。孔子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谓性。亦是说气质之性也。夫书及孔孟之言。非但无气质之性四字。又何尝有气质字乎。然而朱子以为说气质之性。而当时及后世之人。无或疑之。今我先师心有二气之说。
阳善阴恶。又以类分。其所谓阳善者。非道心乎。其所谓阴恶者。非人心乎。若使心气为一而已。则何以有阳善阴恶之分乎。此则吾辈今日之说。未尝不合于朱子之意者也。若夫朱子以主张气字。斥季通者。观其夜气之谕。可知季通所主张者。气质而非心气也。是则恐非所可疑也。未知高明以为如何。噫。若非吾兄之善发问。何以罄竭愚见至此耶。抑有慨惜于朴兄者。自古圣贤随时立教。其言自有所不能尽同者。故大学言明德。而中庸言性。则是其言不同也。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人无有不善。则是其言亦不同也。然而先儒不以为疑。今吾朴兄。乃以心有二气之论。少异前贤之言。大加疑怪。若使朴兄生于程朱以前。则安知其不以曾思孔孟之言为疑乎。且夫气质之性四字。前圣之所未尝言者。而程张始发之。此非可疑之大者乎。然而朱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又曰。气质之性。古人虽不曾与人说著。考之经典。却有此意。如书云人惟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与夫天乃锡王勇智之说。皆此意也。孔子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谓性。亦是说气质之性也。夫书及孔孟之言。非但无气质之性四字。又何尝有气质字乎。然而朱子以为说气质之性。而当时及后世之人。无或疑之。今我先师心有二气之说。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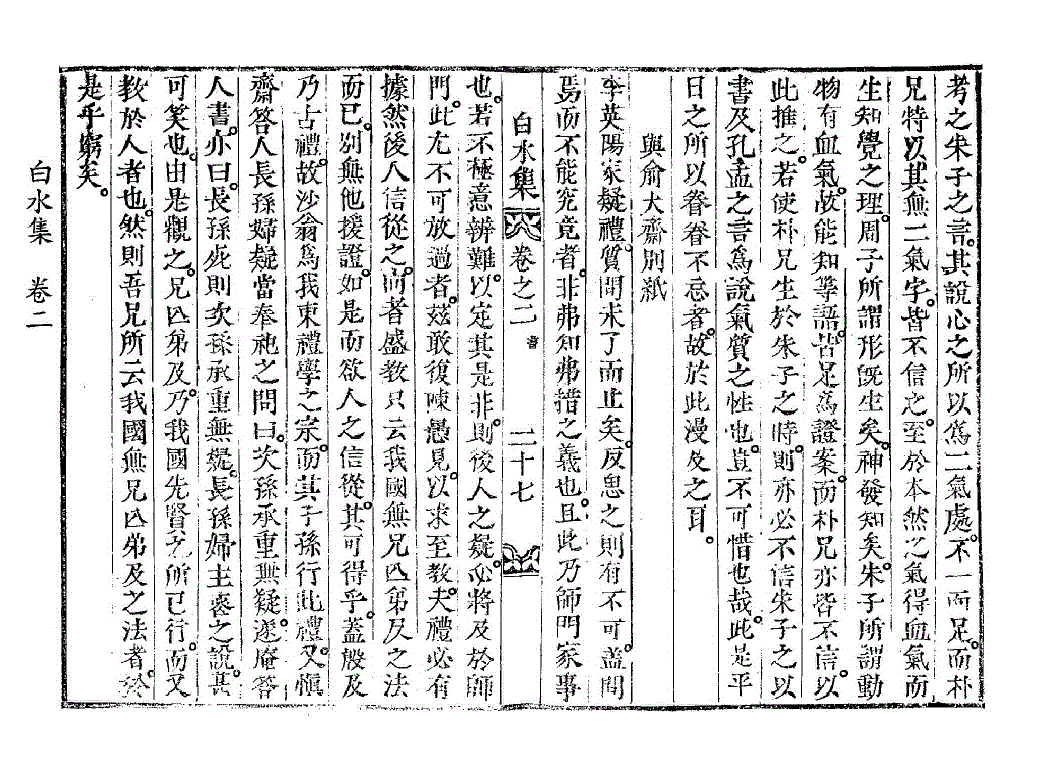 考之朱子之言。其说心之所以为二气处。不一而足。而朴兄特以其无二气字。皆不信之。至于本然之气得血气而生知觉之理。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朱子所谓动物有血气。故能知等语。皆足为證案。而朴兄亦皆不信。以此推之。若使朴兄生于朱子之时。则亦必不信朱子之以书及孔,孟之言为说气质之性也。岂不可惜也哉。此是平日之所以眷眷不忘者。故于此漫及之耳。
考之朱子之言。其说心之所以为二气处。不一而足。而朴兄特以其无二气字。皆不信之。至于本然之气得血气而生知觉之理。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朱子所谓动物有血气。故能知等语。皆足为證案。而朴兄亦皆不信。以此推之。若使朴兄生于朱子之时。则亦必不信朱子之以书及孔,孟之言为说气质之性也。岂不可惜也哉。此是平日之所以眷眷不忘者。故于此漫及之耳。与俞大斋别纸
李英阳家疑礼。质问未了而止矣。反思之则有不可。盖问焉而不能究竟者。非弗知弗措之义也。且此乃师门家事也。若不极意辨难。以定其是非。则后人之疑。必将及于师门。此尤不可放过者。玆敢复陈愚见。以求至教。夫礼必有据然后人信从之。向者盛教只云我国无兄亡弟及之法而已。别无他援證。如是而欲人之信从。其可得乎。盖殷及乃古礼。故沙翁为我东礼学之宗。而其子孙行此礼。又慎斋答人长孙妇疑当奉祀之问曰。次孙承重无疑。遂庵答人书。亦曰。长孙死则次孙承重无疑。长孙妇主丧之说。甚可笑也。由是观之。兄亡弟及。乃我国先贤之所已行。而又教于人者也。然则吾兄所云我国无兄亡弟及之法者。于是乎穷矣。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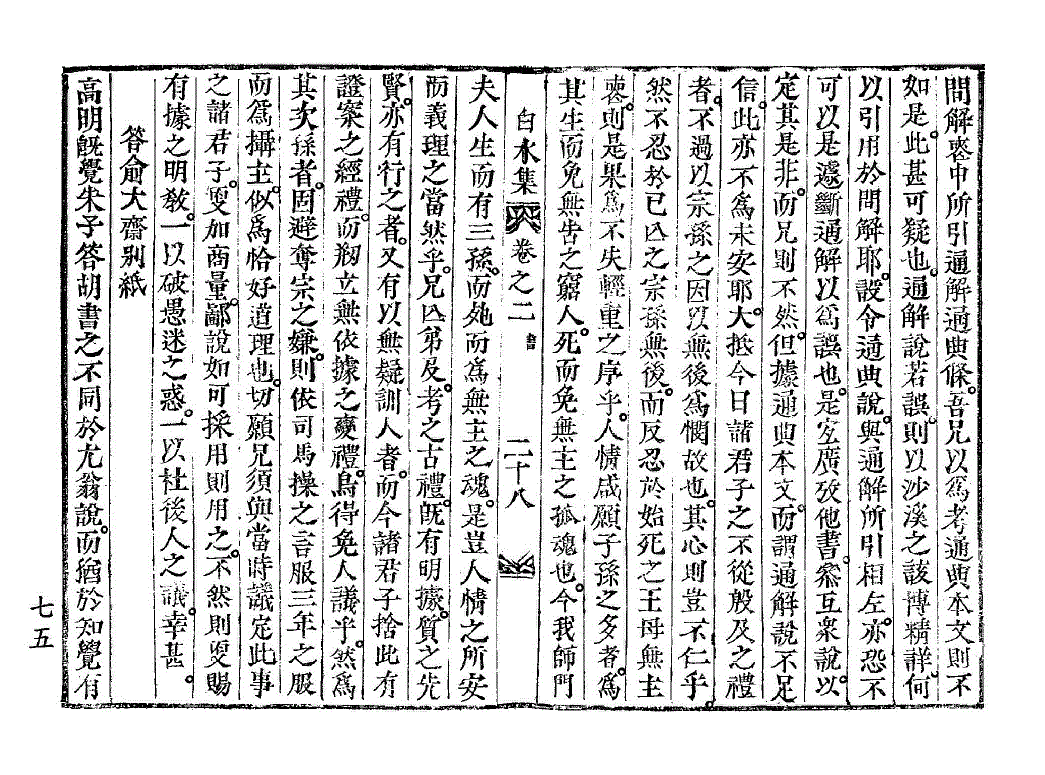 问解丧中所引通解通典条。吾兄以为考通典本文则不如是。此甚可疑也。通解说若误。则以沙溪之该博精详。何以引用于问解耶。设令通典说。与通解所引相左。亦恐不可以是遽断通解以为误也。是宜广考他书。参互众说。以定其是非。而兄则不然。但据通典本文。而谓通解说不足信。此亦不为未安耶。大抵今日诸君子之不从殷及之礼者。不过以宗孙之因以无后为悯故也。其心则岂不仁乎。然不忍于已亡之宗孙无后。而反忍于始死之王母无主丧。则是果为不失轻重之序乎。人情咸愿子孙之多者。为其生而免无告之穷人。死而免无主之孤魂也。今我师门夫人生而有三孙。而死而为无主之魂。是岂人情之所安而义理之当然乎。兄亡弟及。考之古礼。既有明据。质之先贤。亦有行之者。又有以无疑训人者。而今诸君子舍此有證案之经礼。而刱立无依据之变礼。乌得免人议乎。然为其次孙者。固避夺宗之嫌。则依司马操之言服三年之服而为摄主。似为恰好道理也。切愿兄须与当时议定此事之诸君子。更加商量。鄙说如可采用则用之。不然则更赐有据之明教。一以破愚迷之惑。一以杜后人之议。幸甚。
问解丧中所引通解通典条。吾兄以为考通典本文则不如是。此甚可疑也。通解说若误。则以沙溪之该博精详。何以引用于问解耶。设令通典说。与通解所引相左。亦恐不可以是遽断通解以为误也。是宜广考他书。参互众说。以定其是非。而兄则不然。但据通典本文。而谓通解说不足信。此亦不为未安耶。大抵今日诸君子之不从殷及之礼者。不过以宗孙之因以无后为悯故也。其心则岂不仁乎。然不忍于已亡之宗孙无后。而反忍于始死之王母无主丧。则是果为不失轻重之序乎。人情咸愿子孙之多者。为其生而免无告之穷人。死而免无主之孤魂也。今我师门夫人生而有三孙。而死而为无主之魂。是岂人情之所安而义理之当然乎。兄亡弟及。考之古礼。既有明据。质之先贤。亦有行之者。又有以无疑训人者。而今诸君子舍此有證案之经礼。而刱立无依据之变礼。乌得免人议乎。然为其次孙者。固避夺宗之嫌。则依司马操之言服三年之服而为摄主。似为恰好道理也。切愿兄须与当时议定此事之诸君子。更加商量。鄙说如可采用则用之。不然则更赐有据之明教。一以破愚迷之惑。一以杜后人之议。幸甚。答俞大斋别纸
高明既觉朱子答胡书之不同于尤翁说。而犹于知觉有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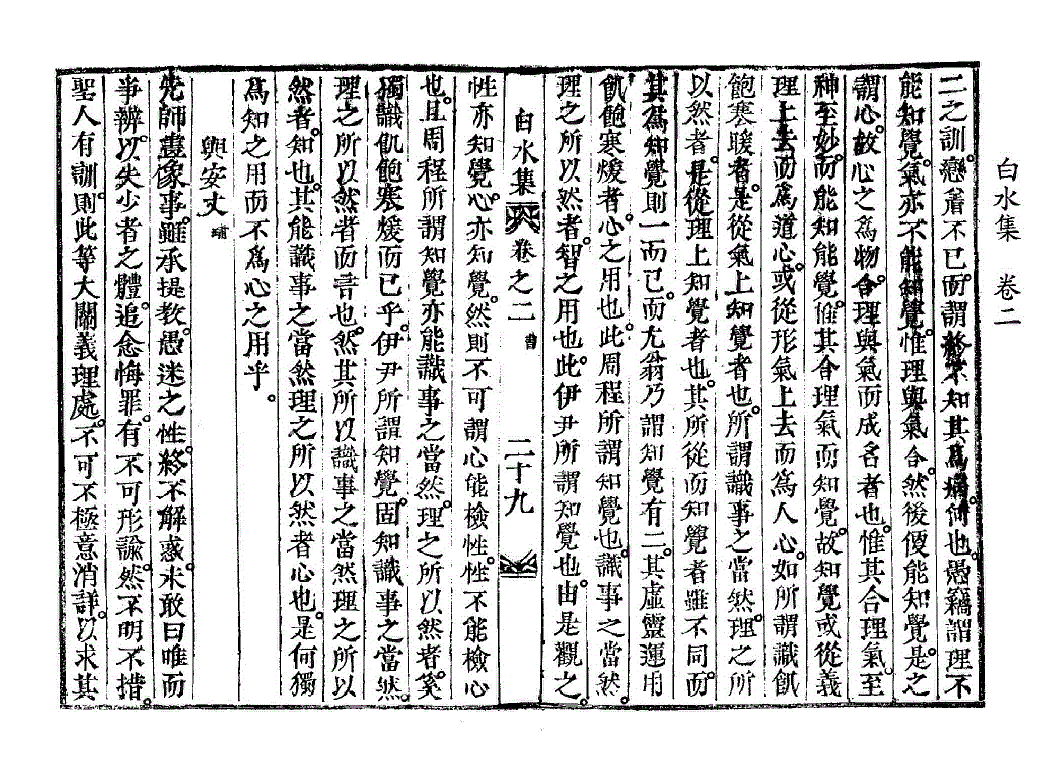 二之训。恋着不已。而谓终不知其为病。何也。愚窃谓理不能知觉。气亦不能知觉。惟理与气合。然后便能知觉。是之谓心。故心之为物。合理与气而成名者也。惟其合理气。至神至妙。而能知能觉。惟其合理气而知觉。故知觉或从义理上去而为道心。或从形气上去而为人心。如所谓识饥饱寒暖者。是从气上知觉者也。所谓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是从理上知觉者也。其所从而知觉者虽不同。而其为知觉则一而已。而尤翁乃谓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饥饱寒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由是观之。性亦知觉。心亦知觉。然则不可谓心能检性。性不能检心也。且周程所谓知觉亦能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奚独识饥饱寒煖而已乎。伊尹所谓知觉。固知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而言也。然其所以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知也。其能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心也。是何独为知之用而不为心之用乎。
二之训。恋着不已。而谓终不知其为病。何也。愚窃谓理不能知觉。气亦不能知觉。惟理与气合。然后便能知觉。是之谓心。故心之为物。合理与气而成名者也。惟其合理气。至神至妙。而能知能觉。惟其合理气而知觉。故知觉或从义理上去而为道心。或从形气上去而为人心。如所谓识饥饱寒暖者。是从气上知觉者也。所谓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是从理上知觉者也。其所从而知觉者虽不同。而其为知觉则一而已。而尤翁乃谓知觉有二。其虚灵运用饥饱寒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谓知觉也。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谓知觉也。由是观之。性亦知觉。心亦知觉。然则不可谓心能检性。性不能检心也。且周程所谓知觉亦能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奚独识饥饱寒煖而已乎。伊尹所谓知觉。固知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而言也。然其所以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知也。其能识事之当然理之所以然者心也。是何独为知之用而不为心之用乎。与安丈(璛)
先师画像事。虽承提教。愚迷之性。终不解惑。未敢曰唯而争辨。以失少者之体。追念悔罪。有不可形谕。然不明不措。圣人有训。则此等大关义理处。不可不极意消详。以求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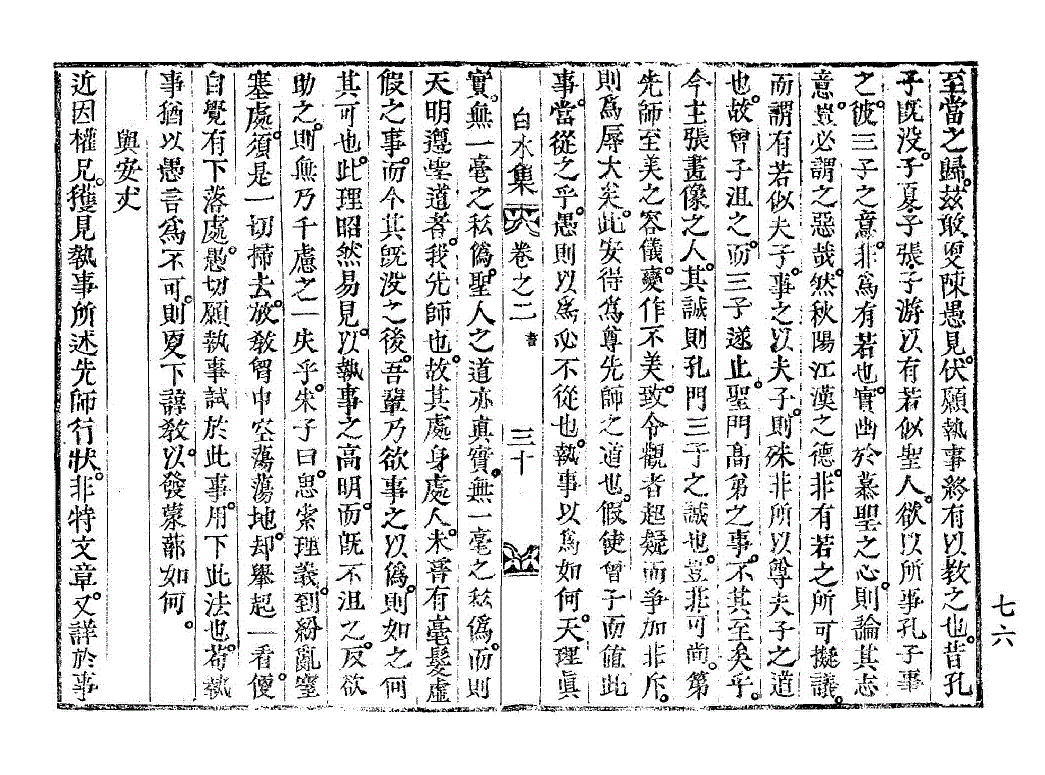 至当之归。玆敢更陈愚见。伏愿执事终有以教之也。昔孔子既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彼三子之意。非为有若也。实出于慕圣之心。则论其志意。岂必谓之恶哉。然秋阳江汉之德。非有若之所可拟议。而谓有若似夫子。事之以夫子。则殊非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故曾子沮之。而三子遂止。圣门高弟之事。不其至矣乎。今主张画像之人。其诚则孔门三子之诚也。岂非可尚。第先师至美之容仪。变作不美。致令观者起疑而争加非斥。则为辱大矣。此安得为尊先师之道也。假使曾子而值此事。当从之乎。愚则以为必不从也。执事以为如何。天理真实。无一毫之私伪。圣人之道亦真实。无一毫之私伪。而则天明遵圣道者。我先师也。故其处身处人。未尝有毫发虚假之事。而今其既没之后。吾辈乃欲事之以伪。则如之何其可也。此理昭然易见。以执事之高明。而既不沮之。反欲助之。则无乃千虑之一失乎。朱子曰。思索理义。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却举起一看。便自觉有下落处。愚切愿执事试于此事。用下此法也。苟执事犹以愚言为不可。则更下谆教。以发蒙蔀如何。
至当之归。玆敢更陈愚见。伏愿执事终有以教之也。昔孔子既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彼三子之意。非为有若也。实出于慕圣之心。则论其志意。岂必谓之恶哉。然秋阳江汉之德。非有若之所可拟议。而谓有若似夫子。事之以夫子。则殊非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故曾子沮之。而三子遂止。圣门高弟之事。不其至矣乎。今主张画像之人。其诚则孔门三子之诚也。岂非可尚。第先师至美之容仪。变作不美。致令观者起疑而争加非斥。则为辱大矣。此安得为尊先师之道也。假使曾子而值此事。当从之乎。愚则以为必不从也。执事以为如何。天理真实。无一毫之私伪。圣人之道亦真实。无一毫之私伪。而则天明遵圣道者。我先师也。故其处身处人。未尝有毫发虚假之事。而今其既没之后。吾辈乃欲事之以伪。则如之何其可也。此理昭然易见。以执事之高明。而既不沮之。反欲助之。则无乃千虑之一失乎。朱子曰。思索理义。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却举起一看。便自觉有下落处。愚切愿执事试于此事。用下此法也。苟执事犹以愚言为不可。则更下谆教。以发蒙蔀如何。与安丈
近因权兄。获见执事所述先师行状。非特文章。又详于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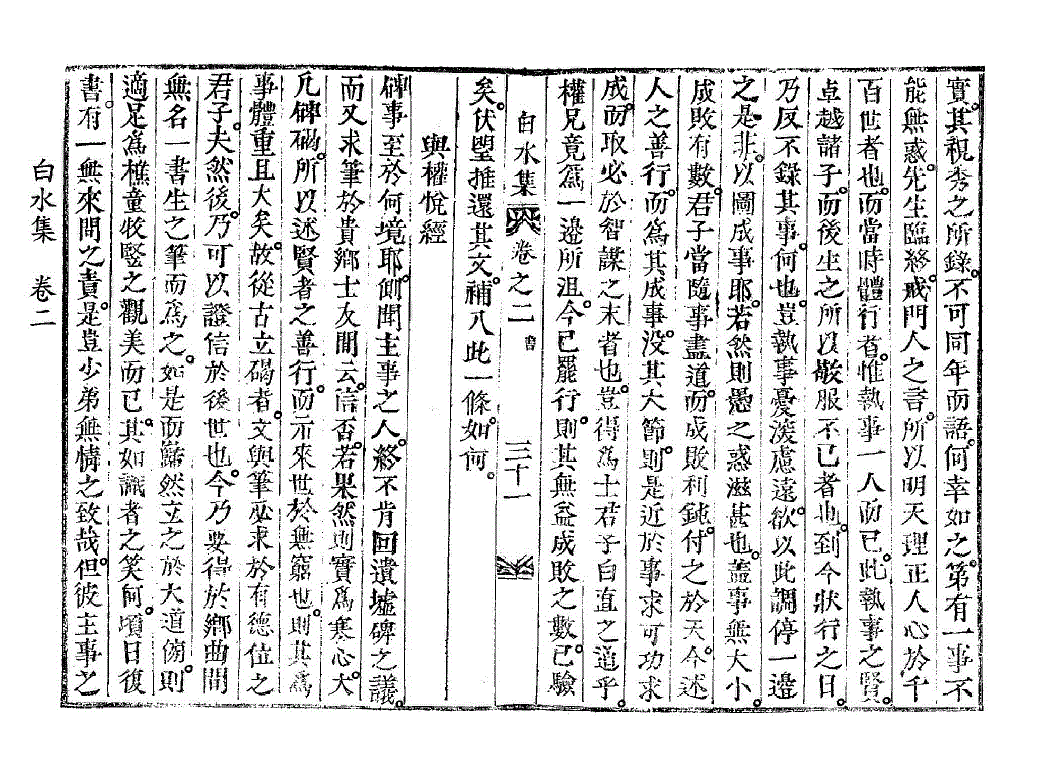 实。其视秀之所录。不可同年而语。何幸如之。第有一事不能无惑。先生临终。戒门人之言。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于千百世者也。而当时体行者。惟执事一人而已。此执事之贤。卓越诸子。而后生之所以敬服不已者也。到今状行之日。乃反不录其事。何也。岂执事忧深虑远。欲以此调停一边之是非。以图成事耶。若然则愚之惑滋甚也。盖事无大小。成败有数。君子当随事尽道。而成败利钝。付之于天。今述人之善行。而为其成事。没其大节。则是近于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于智谋之末者也。岂得为士君子白直之道乎。权兄竟为一边所沮。今已罢行。则其无益成败之数。已验矣。伏望推还其文。补入此一条。如何。
实。其视秀之所录。不可同年而语。何幸如之。第有一事不能无惑。先生临终。戒门人之言。所以明天理正人心于千百世者也。而当时体行者。惟执事一人而已。此执事之贤。卓越诸子。而后生之所以敬服不已者也。到今状行之日。乃反不录其事。何也。岂执事忧深虑远。欲以此调停一边之是非。以图成事耶。若然则愚之惑滋甚也。盖事无大小。成败有数。君子当随事尽道。而成败利钝。付之于天。今述人之善行。而为其成事。没其大节。则是近于事求可功求成。而取必于智谋之末者也。岂得为士君子白直之道乎。权兄竟为一边所沮。今已罢行。则其无益成败之数。已验矣。伏望推还其文。补入此一条。如何。与权悦经
碑事至于何境耶。侧闻主事之人。终不肯回遗墟碑之议。而又求笔于贵乡士友间云。信否。若果然则实为寒心。大凡碑碣。所以述贤者之善行。而示来世于无穷也。则其为事体重且大矣。故从古立碣者。文与笔必求于有德位之君子。夫然后。乃可以證信于后世也。今乃要得于乡曲间无名一书生之笔而为之。如是而岿然立之于大道傍。则适足为樵童牧竖之观美而已。其如识者之笑何。顷日复书。有一无来问之责。是岂少弟无情之致哉。但彼主事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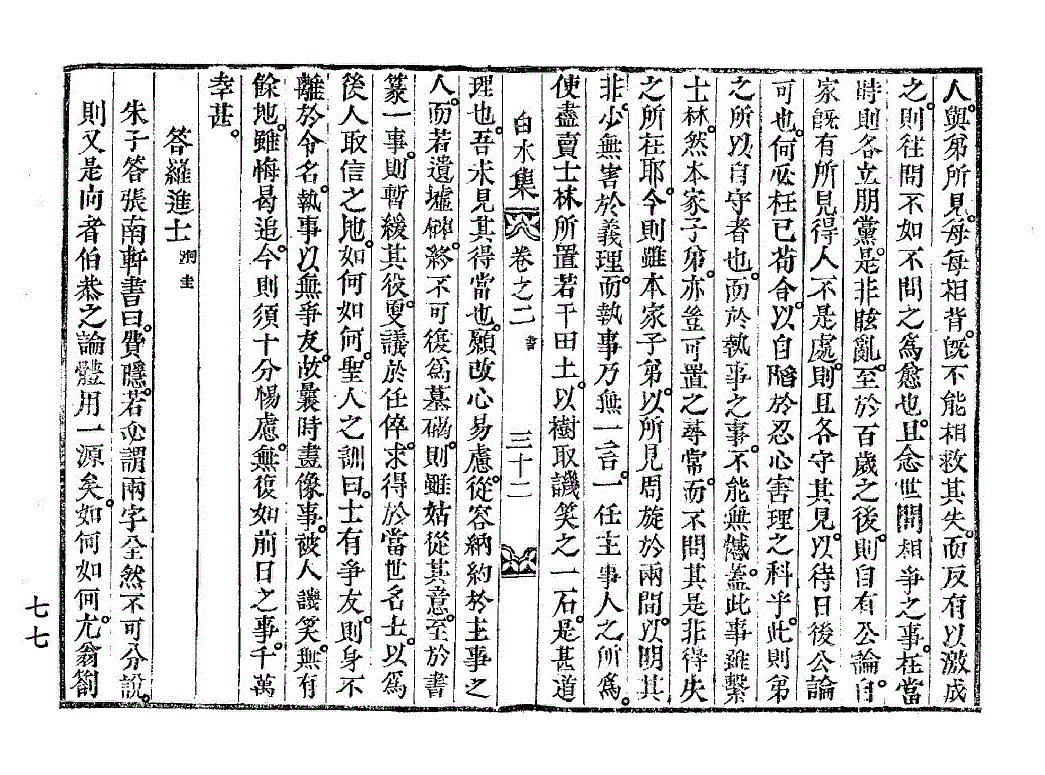 人。与弟所见。每每相背。既不能相救其失。而反有以激成之。则往问不如不问之为愈也。且念世间相争之事。在当时则各立朋党。是非眩乱。至于百岁之后。则自有公论。自家既有所见得人不是处。则且各守其见。以待日后公论可也。何必枉己苟合。以自陷于忍心害理之科乎。此则弟之所以自守者也。而于执事之事。不能无憾。盖此事虽系士林。然本家子弟。亦岂可置之寻常。而不问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耶。今则虽本家子弟。以所见周旋于两间。以明其非。少无害于义理。而执事乃无一言。一任主事人之所为。使尽卖士林所置若干田土。以树取讥笑之一石。是甚道理也。吾未见其得当也。愿改心易虑。从容纳约于主事之人。而若遗墟碑。终不可复为墓碣。则虽姑从其意。至于书篆一事。则暂缓其役。更议于任倅。求得于当世名士。以为后人取信之地。如何如何。圣人之训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执事以无争友。故曩时画像事。被人讥笑。无有馀地。虽悔曷追。今则须十分惕虑。无复如前日之事。千万幸甚。
人。与弟所见。每每相背。既不能相救其失。而反有以激成之。则往问不如不问之为愈也。且念世间相争之事。在当时则各立朋党。是非眩乱。至于百岁之后。则自有公论。自家既有所见得人不是处。则且各守其见。以待日后公论可也。何必枉己苟合。以自陷于忍心害理之科乎。此则弟之所以自守者也。而于执事之事。不能无憾。盖此事虽系士林。然本家子弟。亦岂可置之寻常。而不问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耶。今则虽本家子弟。以所见周旋于两间。以明其非。少无害于义理。而执事乃无一言。一任主事人之所为。使尽卖士林所置若干田土。以树取讥笑之一石。是甚道理也。吾未见其得当也。愿改心易虑。从容纳约于主事之人。而若遗墟碑。终不可复为墓碣。则虽姑从其意。至于书篆一事。则暂缓其役。更议于任倅。求得于当世名士。以为后人取信之地。如何如何。圣人之训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执事以无争友。故曩时画像事。被人讥笑。无有馀地。虽悔曷追。今则须十分惕虑。无复如前日之事。千万幸甚。答罗进士(炯圭)
朱子答张南轩书曰。费隐。若必谓两字全然不可分说。则又是向者伯恭之论体用一源矣。如何如何。尤翁劄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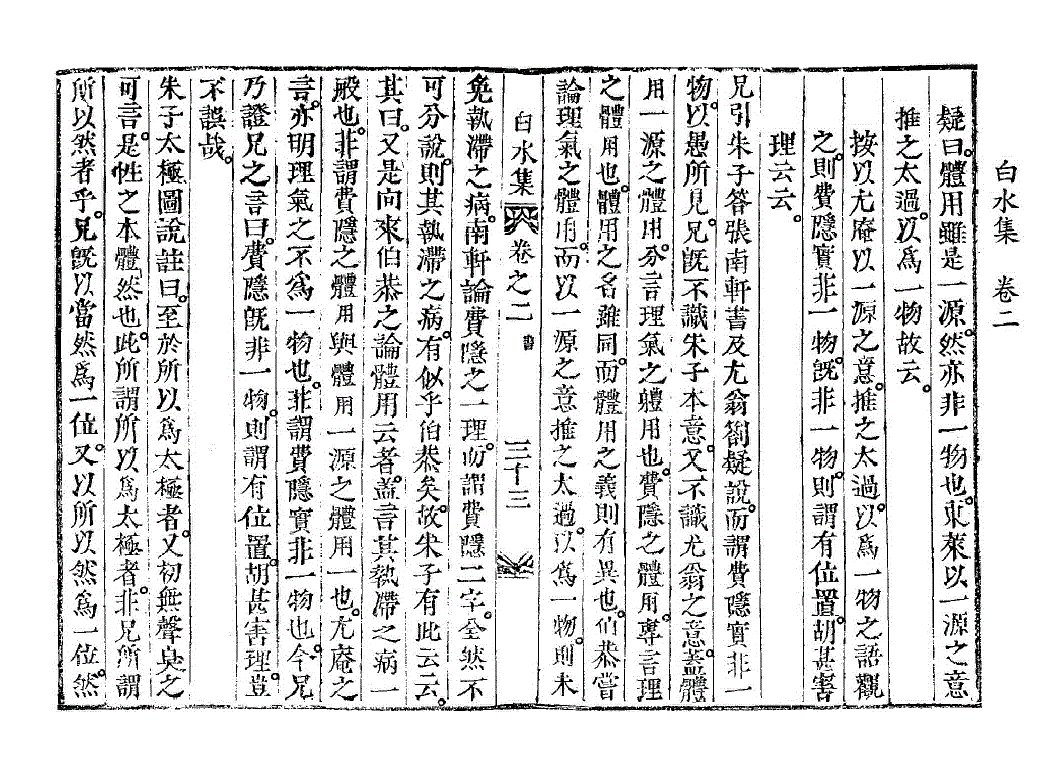 疑曰。体用虽是一源。然亦非一物也。东莱以一源之意推之太过。以为一物故云。
疑曰。体用虽是一源。然亦非一物也。东莱以一源之意推之太过。以为一物故云。按以尤庵以一源之意。推之太过。以为一物之语观之。则费隐实非一物。既非一物。则谓有位置。胡甚害理云云。
兄引朱子答张南轩书及尤翁劄疑说。而谓费隐实非一物。以愚所见。兄既不识朱子本意。又不识尤翁之意。盖体用一源之体用。分言理气之体用也。费隐之体用。专言理之体用也。体用之名虽同。而体用之义则有异也。伯恭尝论理气之体用。而以一源之意推之太过。以为一物。则未免执滞之病。南轩论费隐之一理。而谓费隐二字。全然不可分说。则其执滞之病。有似乎伯恭矣。故朱子有此云云。其曰。又是向来伯恭之论体用云者。盖言其执滞之病一般也。非谓费隐之体用与体用一源之体用一也。尤庵之言。亦明理气之不为一物也。非谓费隐实非一物也。今兄乃證兄之言曰。费隐既非一物。则谓有位置。胡甚害理。岂不误哉。
朱子太极图说注曰。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此所谓所以为太极者。非兄所谓所以然者乎。兄既以当然为一位。又以所以然为一位。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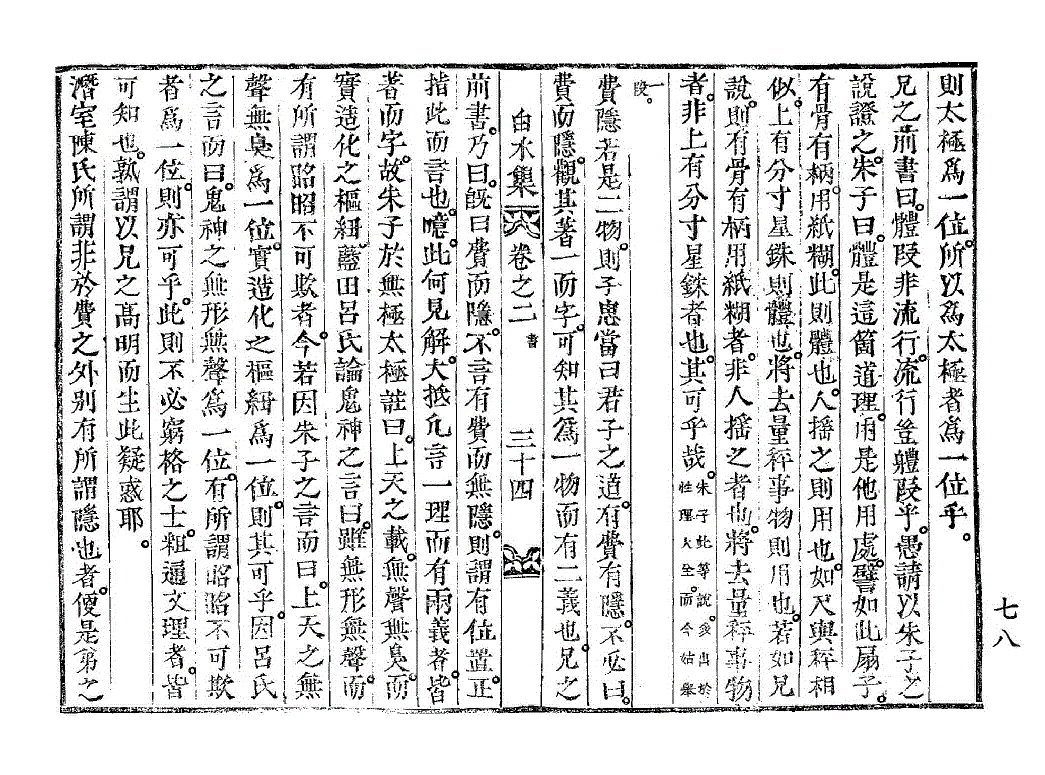 则太极为一位。所以为太极者为一位乎。
则太极为一位。所以为太极者为一位乎。兄之前书曰。体段非流行。流行岂体段乎。愚请以朱子之说證之。朱子曰。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如尺与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铢则体也。将去量秤事物则用也。若如兄说。则有骨有柄用纸糊者。非人摇之者也。将去量秤事物者。非上有分寸星铢者也。其可乎哉。(朱子此等说。多出于性理大全。而今姑举一段。)
费隐若是二物。则子思当曰君子之道。有费有隐。不必曰。费而隐。观其著一而字。可知其为一物而有二义也。兄之前书。乃曰。既曰费而隐。不言有费而无隐。则谓有位置。正指此而言也。噫。此何见解。大抵凡言一理而有两义者。皆著而字。故朱子于无极太极注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蓝田吕氏论鬼神之言曰。虽无形无声。而有所谓昭昭不可欺者。今若因朱子之言而曰。上天之无声无臭为一位。实造化之枢纽为一位。则其可乎。因吕氏之言而曰。鬼神之无形无声为一位。有所谓昭昭不可欺者为一位。则亦可乎。此则不必穷格之士。粗通文理者。皆可知也。孰谓以兄之高明而生此疑惑耶。
潜室陈氏所谓非于费之外别有所谓隐也者。便是弟之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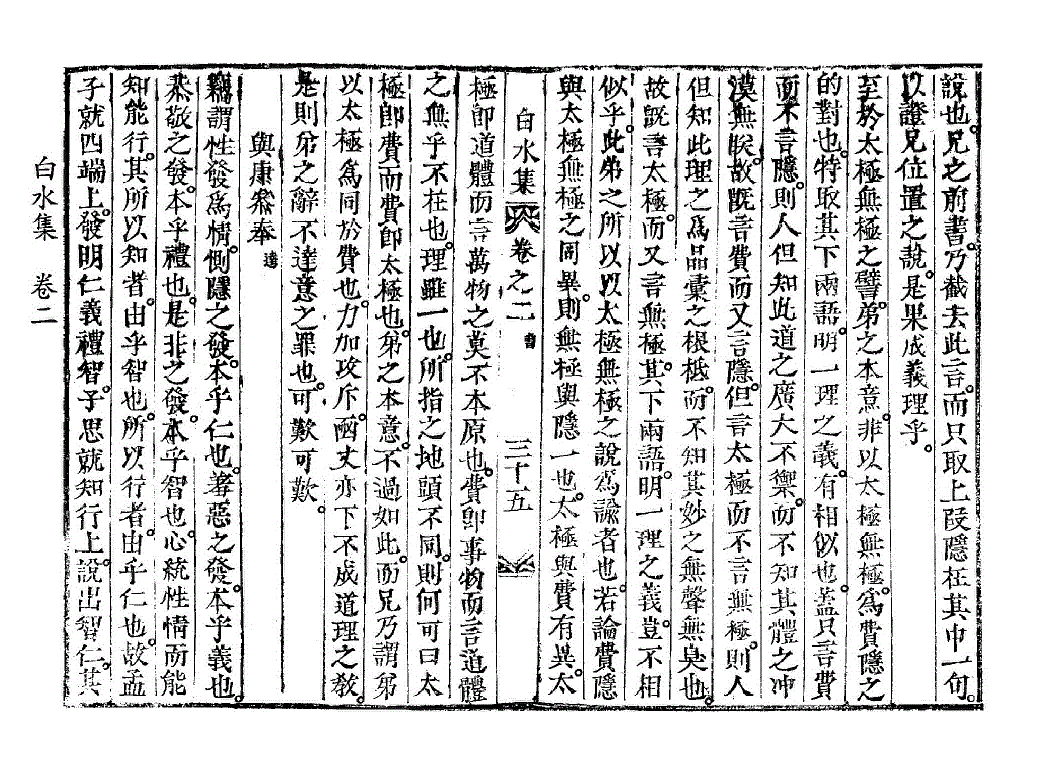 说也。兄之前书。乃截去此言。而只取上段隐在其中一句。以證兄位置之说。是果成义理乎。
说也。兄之前书。乃截去此言。而只取上段隐在其中一句。以證兄位置之说。是果成义理乎。至于太极无极之譬。弟之本意。非以太极无极。为费隐之的对也。特取其下两语。明一理之义。有相似也。盖只言费而不言隐。则人但知此道之广大不御。而不知其体之冲漠无眹。故既言费而又言隐。但言太极而不言无极。则人但知此理之为品汇之根柢。而不知其妙之无声无臭也。故既言太极。而又言无极。其下两语。明一理之义。岂不相似乎。此弟之所以以太极无极之说为谕者也。若论费隐与太极无极之同异。则无极与隐一也。太极与费有异。太极即道体而言万物之莫不本原也。费即事物而言道体之无乎不在也。理虽一也。所指之地头不同。则何可曰太极即费而费即太极也。弟之本意。不过如此。而兄乃谓弟以太极为同于费也。力加攻斥。函丈亦下不成道理之教。是则弟之辞不达意之罪也。可叹可叹。
与康参奉(逵)
窃谓性发为情。恻隐之发。本乎仁也。羞恶之发。本乎义也。恭敬之发。本乎礼也。是非之发。本乎智也。心统性情而能知能行。其所以知者。由乎智也。所以行者。由乎仁也。故孟子就四端上。发明仁义礼智。子思就知行上。说出智仁。其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7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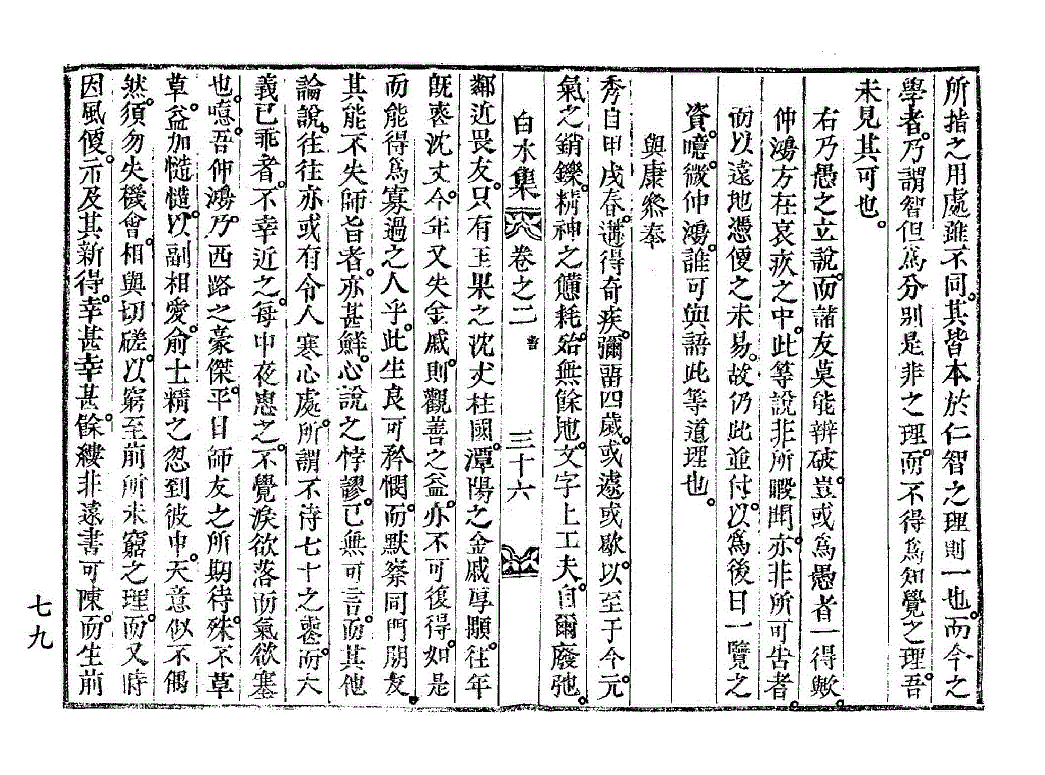 所指之用处虽不同。其皆本于仁智之理则一也。而今之学者。乃谓智但为分别是非之理。而不得为知觉之理。吾未见其可也。
所指之用处虽不同。其皆本于仁智之理则一也。而今之学者。乃谓智但为分别是非之理。而不得为知觉之理。吾未见其可也。右乃愚之立说。而诸友莫能辨破。岂或为愚者一得欤。仲鸿方在哀疚之中。此等说非所暇闻。亦非所可告者。而以远地凭便之未易。故仍此并付。以为后日一览之资。噫。微仲鸿。谁可与语此等道理也。
与康参奉
秀自甲戌春。遘得奇疾。弥留四岁。或遽或歇。以至于今。元气之销铄。精神之惫耗。殆无馀地。文字上工夫。自尔废弛。邻近畏友。只有玉果之沈丈柱国。潭阳之金戚厚颙。往年既丧沈丈。今年又失金戚。则观善之益。亦不可复得。如是而能得为寡过之人乎。此生良可矜悯。而默察同门朋友。其能不失师旨者。亦甚鲜。心说之悖谬。已无可言。而其他论说。往往亦或有令人寒心处。所谓不待七十之丧。而大义已乖者。不幸近之。每中夜思之。不觉泪欲落而气欲塞也。噫。吾仲鸿。乃西路之豪杰。平日师友之所期待。殊不草草。益加慥慥。以副相爱。俞士精之忽到彼中。天意似不偶然。须勿失机会。相与切磋。以穷至前所未穷之理。而又时因风便。示及其新得。幸甚幸甚。馀缕非远书可陈。而生前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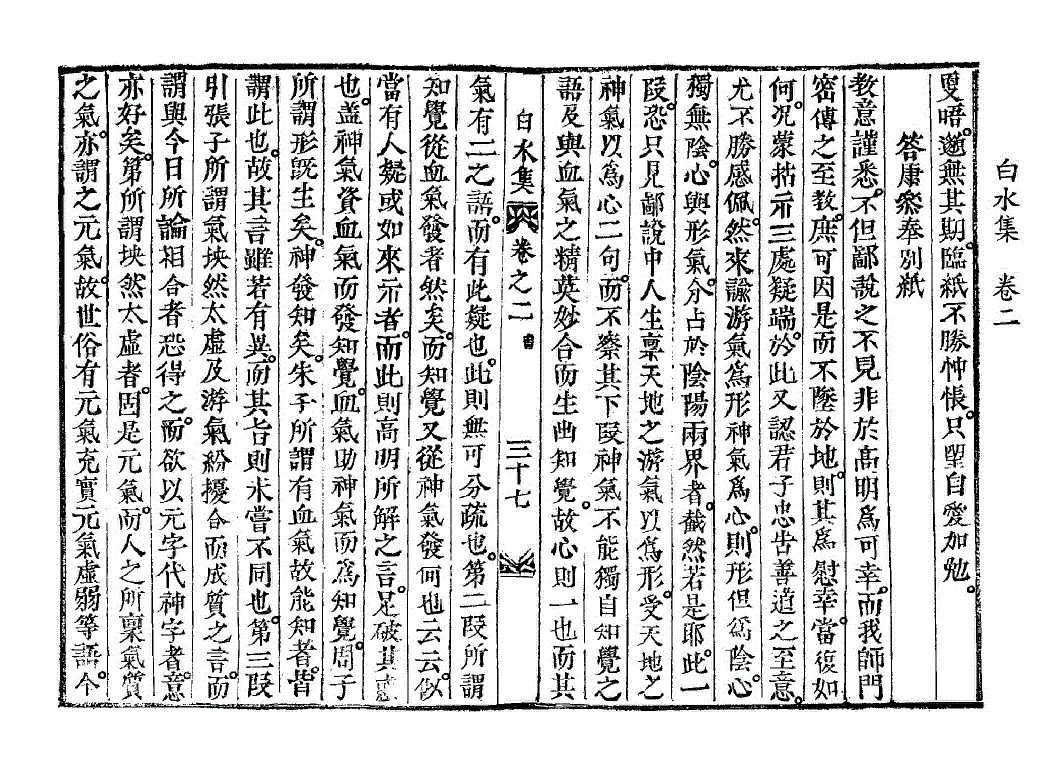 更唔。邈无其期。临纸不胜忡怅。只望自爱加勉。
更唔。邈无其期。临纸不胜忡怅。只望自爱加勉。答康参奉别纸
教意谨悉。不但鄙说之不见非于高明为可幸。而我师门密传之至教。庶可因是而不坠于地。则其为慰幸。当复如何。况蒙拈示三处疑端。于此又认君子忠告善道之至意。尤不胜感佩。然来谕游气为形神气为心。则形但为阴。心独无阴。心与形气。分占于阴阳两界者。截然若是耶。此一段。恐只见鄙说中人生禀天地之游气以为形。受天地之神气以为心二句。而不察其下段神气不能独自知觉之语及与血气之精英妙合而生出知觉。故心则一也而其气有二之语。而有此疑也。此则无可分疏也。第二段所谓知觉从血气发者然矣。而知觉又从神气发何也云云。似当有人疑或如来示者。而此则高明所解之言。足破其惑也。盖神气资血气而发知觉。血气助神气而为知觉。周子所谓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朱子所谓有血气故能知者。皆谓此也。故其言虽若有异。而其旨则未尝不同也。第三段引张子所谓气坱然太虚及游气纷扰合而成质之言。而谓与今日所论相合者恐得之。而欲以元字代神字者。意亦好矣。第所谓坱然太虚者。固是元气。而人之所禀气质之气。亦谓之元气。故世俗有元气充实元气虚弱等语。今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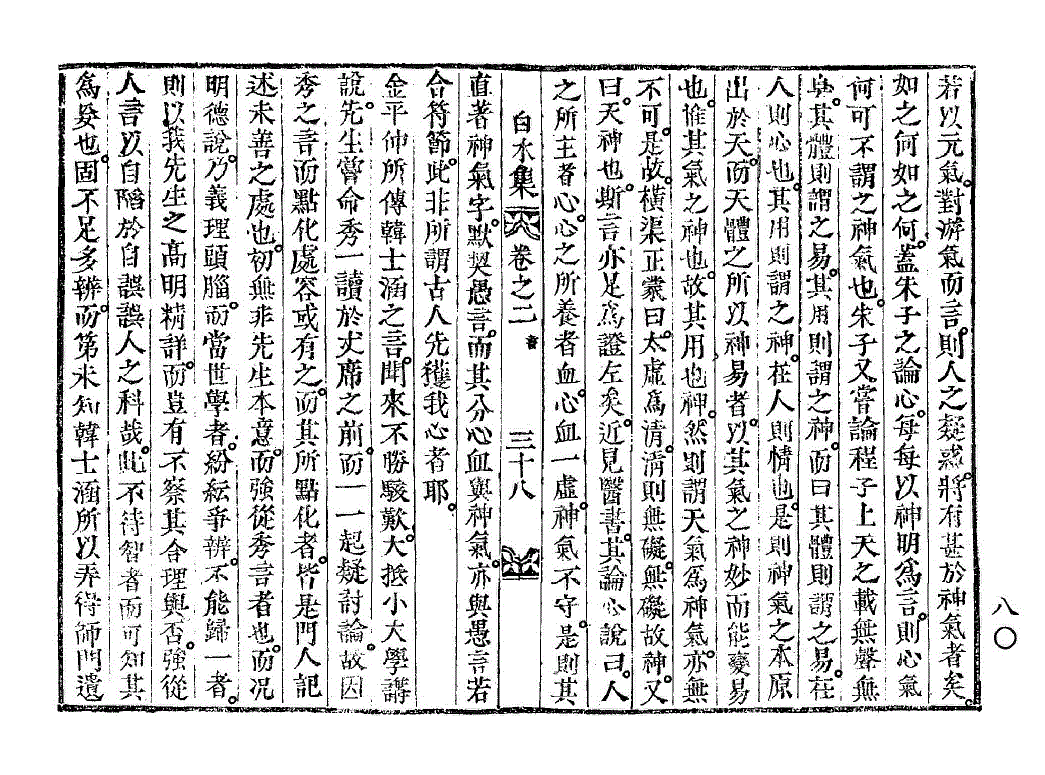 若以元气。对游气而言。则人之疑惑。将有甚于神气者矣。如之何如之何。盖朱子之论心。每每以神明为言。则心气何可不谓之神气也。朱子又尝论程子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用则谓之神。而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是则神气之本原出于天。而天体之所以神易者。以其气之神妙而能变易也。惟其气之神也。故其用也神。然则谓天气为神气。亦无不可。是故。横渠正蒙曰。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又曰。天神也。斯言亦足为證左矣。近见医书。其论心说曰。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是则其直著神气字。默契愚言。而其分心血与神气。亦与愚言若合符节。此非所谓古人先获我心者耶。
若以元气。对游气而言。则人之疑惑。将有甚于神气者矣。如之何如之何。盖朱子之论心。每每以神明为言。则心气何可不谓之神气也。朱子又尝论程子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用则谓之神。而曰其体则谓之易。在人则心也。其用则谓之神。在人则情也。是则神气之本原出于天。而天体之所以神易者。以其气之神妙而能变易也。惟其气之神也。故其用也神。然则谓天气为神气。亦无不可。是故。横渠正蒙曰。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又曰。天神也。斯言亦足为證左矣。近见医书。其论心说曰。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是则其直著神气字。默契愚言。而其分心血与神气。亦与愚言若合符节。此非所谓古人先获我心者耶。金平仲所传韩士涵之言。闻来不胜骇叹。大抵小大学讲说。先生尝命秀一读于丈席之前。而一一起疑讨论。故因秀之言而点化处容或有之。而其所点化者。皆是门人记述未善之处也。初无非先生本意。而强从秀言者也。而况明德说。乃义理头脑。而当世学者。纷纭争辨。不能归一者。则以我先生之高明精详。而岂有不察其合理与否。强从人言以自陷于自误误人之科哉。此不待智者而可知其为妄也。固不足多辨。而第未知韩士涵所以弄得师门遗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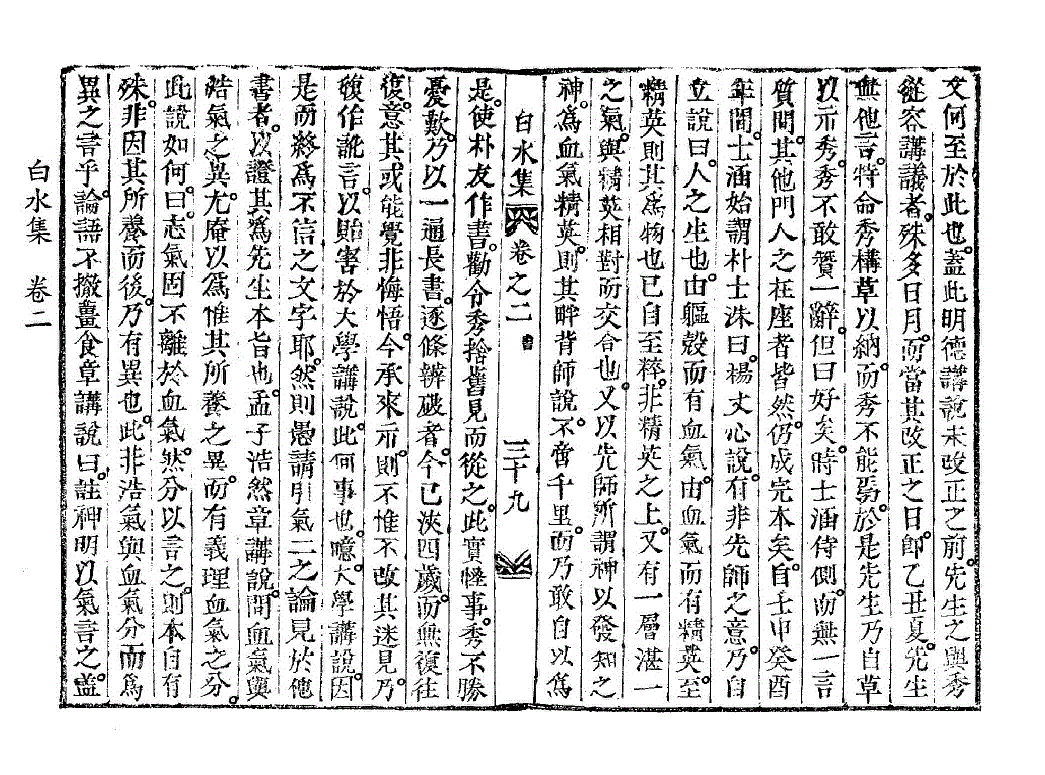 文何至于此也。盖此明德讲说未改正之前。先生之与秀从容讲议者。殊多日月。而当其改正之日。即乙丑夏。先生无他言。特命秀构草以纳。而秀不能焉。于是先生乃自草以示秀。秀不敢赞一辞。但曰好矣。时士涵侍侧。而无一言质问。其他门人之在座者皆然。仍成完本矣。自壬申癸酉年间。士涵始谓朴士洙曰。杨丈心说。有非先师之意。乃自立说曰。人之生也。由躯壳而有血气。由血气而有精英。至精英则其为物也已自至粹。非精英之上。又有一层湛一之气。与精英相对而交合也。又以先师所谓神以发知之神。为血气精英。则其畔背师说。不啻千里。而乃敢自以为是。使朴友作书。劝令秀舍旧见而从之。此实怪事。秀不胜忧叹。乃以一通长书。逐条辨破者。今已浃四岁。而无复往复。意其或能觉非悔悟。今承来示。则不惟不改其迷见。乃复作讹言。以贻害于大学讲说。此何事也。噫。大学讲说。因是而终为不信之文字耶。然则愚请引气二之论见于他书者。以證其为先生本旨也。孟子浩然章讲说。问血气与浩气之异。尤庵以为惟其所养之异。而有义理血气之分。此说如何。曰。志气固不离于血气。然分以言之。则本自有殊。非因其所养而后。乃有异也。此非浩气与血气分而为异之言乎。论语不撤姜食章讲说曰。注神明以气言之。盖
文何至于此也。盖此明德讲说未改正之前。先生之与秀从容讲议者。殊多日月。而当其改正之日。即乙丑夏。先生无他言。特命秀构草以纳。而秀不能焉。于是先生乃自草以示秀。秀不敢赞一辞。但曰好矣。时士涵侍侧。而无一言质问。其他门人之在座者皆然。仍成完本矣。自壬申癸酉年间。士涵始谓朴士洙曰。杨丈心说。有非先师之意。乃自立说曰。人之生也。由躯壳而有血气。由血气而有精英。至精英则其为物也已自至粹。非精英之上。又有一层湛一之气。与精英相对而交合也。又以先师所谓神以发知之神。为血气精英。则其畔背师说。不啻千里。而乃敢自以为是。使朴友作书。劝令秀舍旧见而从之。此实怪事。秀不胜忧叹。乃以一通长书。逐条辨破者。今已浃四岁。而无复往复。意其或能觉非悔悟。今承来示。则不惟不改其迷见。乃复作讹言。以贻害于大学讲说。此何事也。噫。大学讲说。因是而终为不信之文字耶。然则愚请引气二之论见于他书者。以證其为先生本旨也。孟子浩然章讲说。问血气与浩气之异。尤庵以为惟其所养之异。而有义理血气之分。此说如何。曰。志气固不离于血气。然分以言之。则本自有殊。非因其所养而后。乃有异也。此非浩气与血气分而为异之言乎。论语不撤姜食章讲说曰。注神明以气言之。盖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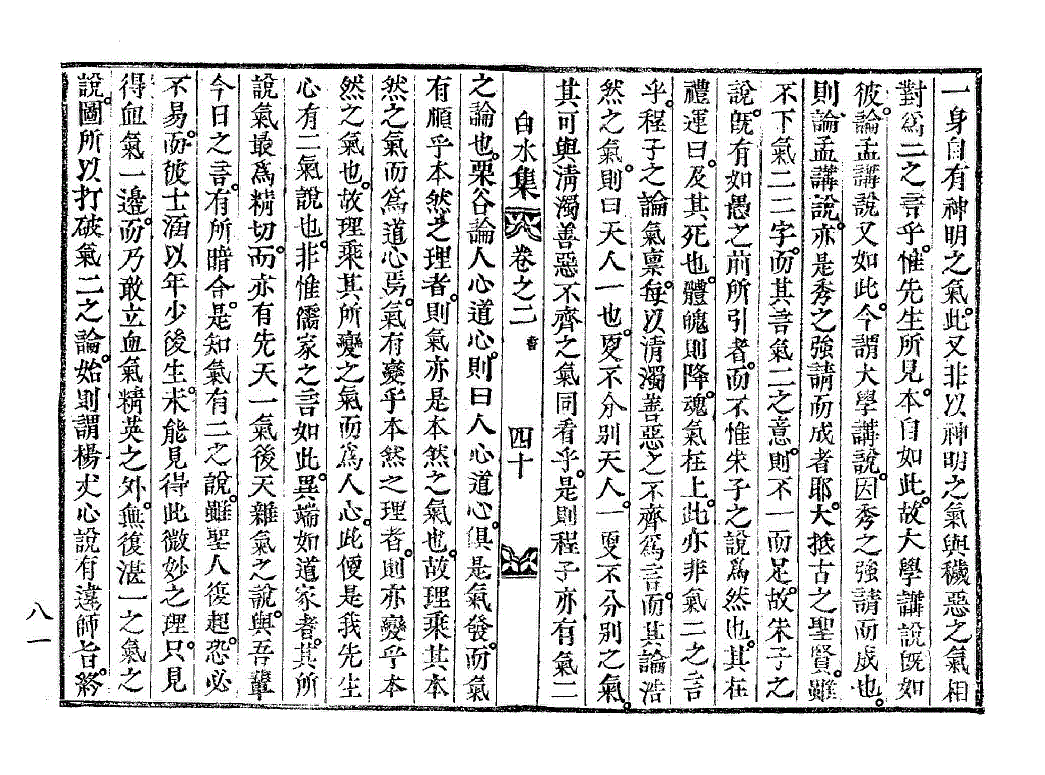 一身自有神明之气。此又非以神明之气与秽恶之气相对为二之言乎。惟先生所见。本自如此。故大学讲说既如彼。论孟讲说又如此。今谓大学讲说。因秀之强请而成也。则论孟讲说。亦是秀之强请而成者耶。大抵古之圣贤。虽不下气二二字。而其言气二之意。则不一而足。故朱子之说。既有如愚之前所引者。而不惟朱子之说为然也。其在礼运曰。及其死也。体魄则降。魂气在上。此亦非气二之言乎。程子之论气禀。每以清浊善恶之不齐为言。而其论浩然之气。则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天人。一更不分别之气。其可与清浊善恶不齐之气同看乎。是则程子亦有气二之论也。栗谷论人心道心。则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此便是我先生心有二气说也。非惟儒家之言如此。异端如道家者。其所说气最为精切。而亦有先天一气后天杂气之说。与吾辈今日之言。有所暗合。是知气有二之说。虽圣人复起。恐必不易。而彼士涵以年少后生。未能见得此微妙之理。只见得血气一边。而乃敢立血气精英之外。无复湛一之气之说。图所以打破气二之论。始则谓杨丈心说有违师旨。终
一身自有神明之气。此又非以神明之气与秽恶之气相对为二之言乎。惟先生所见。本自如此。故大学讲说既如彼。论孟讲说又如此。今谓大学讲说。因秀之强请而成也。则论孟讲说。亦是秀之强请而成者耶。大抵古之圣贤。虽不下气二二字。而其言气二之意。则不一而足。故朱子之说。既有如愚之前所引者。而不惟朱子之说为然也。其在礼运曰。及其死也。体魄则降。魂气在上。此亦非气二之言乎。程子之论气禀。每以清浊善恶之不齐为言。而其论浩然之气。则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天人。一更不分别之气。其可与清浊善恶不齐之气同看乎。是则程子亦有气二之论也。栗谷论人心道心。则曰人心道心。俱是气发。而气有顺乎本然之理者。则气亦是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本然之气而为道心焉。气有变乎本然之理者。则亦变乎本然之气也。故理乘其所变之气而为人心。此便是我先生心有二气说也。非惟儒家之言如此。异端如道家者。其所说气最为精切。而亦有先天一气后天杂气之说。与吾辈今日之言。有所暗合。是知气有二之说。虽圣人复起。恐必不易。而彼士涵以年少后生。未能见得此微妙之理。只见得血气一边。而乃敢立血气精英之外。无复湛一之气之说。图所以打破气二之论。始则谓杨丈心说有违师旨。终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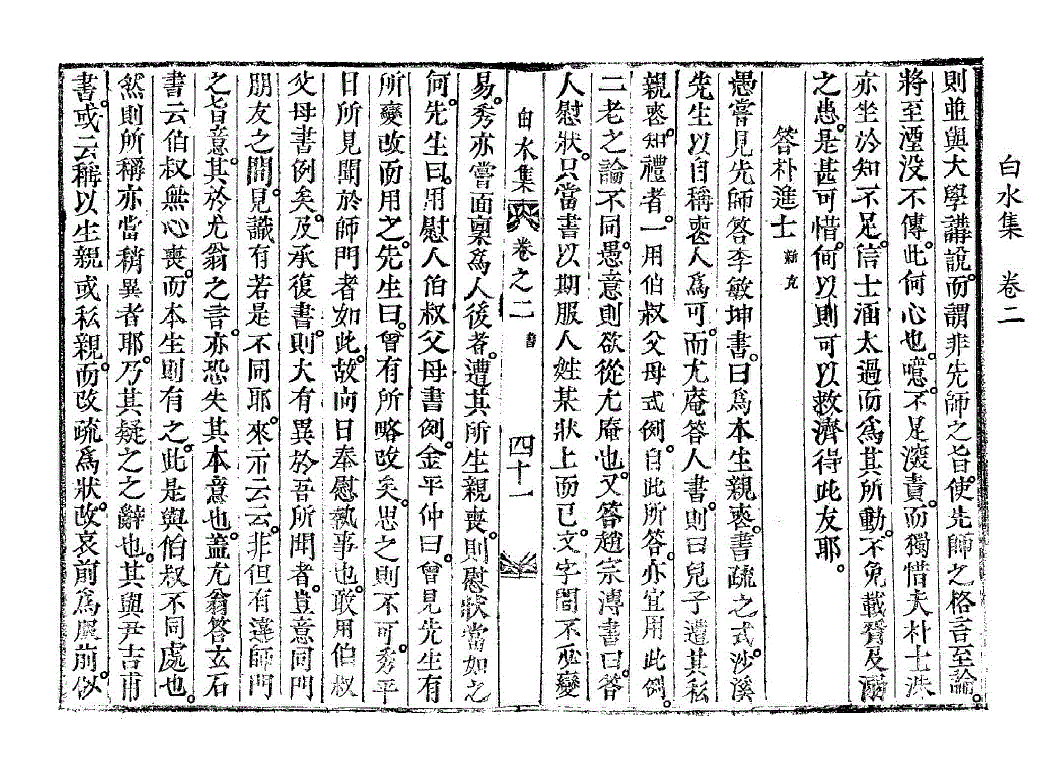 则并与大学讲说。而谓非先师之旨。使先师之格言至论。将至湮没不传。此何心也。噫。不足深责。而独惜夫朴士洙亦坐于知不足。信士涵太过而为其所动。不免载胥及溺之患。是甚可惜。何以则可以救济得此友耶。
则并与大学讲说。而谓非先师之旨。使先师之格言至论。将至湮没不传。此何心也。噫。不足深责。而独惜夫朴士洙亦坐于知不足。信士涵太过而为其所动。不免载胥及溺之患。是甚可惜。何以则可以救济得此友耶。答朴进士(新克)
愚尝见先师答李敏坤书。曰为本生亲丧。书疏之式。沙溪先生以自称丧人为可。而尤庵答人书。则曰儿子遭其私亲丧。知礼者。一用伯叔父母式例。自此所答。亦宜用此例。二老之论不同。愚意则欲从尤庵也。又答赵宗溥书曰。答人慰状。只当书以期服人姓某状上而已。文字间不必变易。秀亦尝面禀为人后者。遭其所生亲丧。则慰状当如之何。先生曰。用慰人伯叔父母书例。金平仲曰。曾见先生有所变改而用之。先生曰。曾有所略改矣。思之则不可。秀平日所见闻于师门者如此。故向日奉慰执事也。敢用伯叔父母书例矣。及承复书。则大有异于吾所闻者。岂意同门朋友之间。见识有若是不同耶。来示云云。非但有违师门之旨意。其于尤翁之言。亦恐失其本意也。盖尤翁答玄石书云伯叔无心丧。而本生则有之。此是与伯叔不同处也。然则所称亦当稍异者耶。乃其疑之之辞也。其与尹吉甫书。或云称以生亲或私亲。而改疏为状。改哀前为服前。似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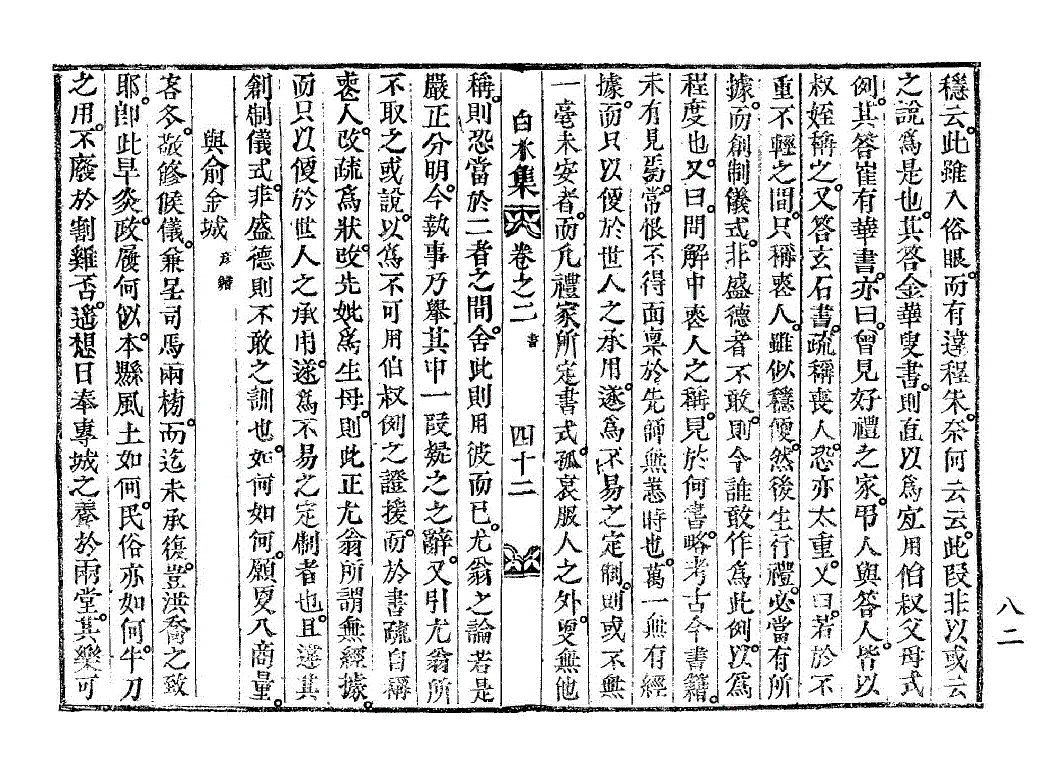 稳云。此虽入俗眼。而有违程朱。奈何云云。此段非以或云之说为是也。其答金华叟书。则直以为宜用伯叔父母式例。其答崔有华书。亦曰。曾见好礼之家。吊人与答人。皆以叔侄称之。又答玄石书。疏称丧人。恐亦太重。又曰。若于不重不轻之间。只称丧人。虽似稳便。然后生行礼。必当有所据。而创制仪式。非盛德者不敢。则今谁敢作为此例。以为程度也。又曰。问解中丧人之称。见于何书。略考古今书籍。未有见焉。常恨不得面禀于先师无恙时也。万一无有经据。而只以便于世人之承用。遂为不易之定制。则或不无一毫未安者。而凡礼家所定书式。孤哀服人之外。更无他称。则恐当于二者之间。舍此则用彼而已。尤翁之论若是严正分明。今执事乃举其中一段疑之之辞。又引尤翁所不取之或说。以为不可用伯叔例之證援。而于书疏自称丧人。改疏为状。改先妣为生母。则此正尤翁所谓无经据。而只以便于世人之承用。遂为不易之定制者也。且违其创制仪式。非盛德则不敢之训也。如何如何。愿更入商量。
稳云。此虽入俗眼。而有违程朱。奈何云云。此段非以或云之说为是也。其答金华叟书。则直以为宜用伯叔父母式例。其答崔有华书。亦曰。曾见好礼之家。吊人与答人。皆以叔侄称之。又答玄石书。疏称丧人。恐亦太重。又曰。若于不重不轻之间。只称丧人。虽似稳便。然后生行礼。必当有所据。而创制仪式。非盛德者不敢。则今谁敢作为此例。以为程度也。又曰。问解中丧人之称。见于何书。略考古今书籍。未有见焉。常恨不得面禀于先师无恙时也。万一无有经据。而只以便于世人之承用。遂为不易之定制。则或不无一毫未安者。而凡礼家所定书式。孤哀服人之外。更无他称。则恐当于二者之间。舍此则用彼而已。尤翁之论若是严正分明。今执事乃举其中一段疑之之辞。又引尤翁所不取之或说。以为不可用伯叔例之證援。而于书疏自称丧人。改疏为状。改先妣为生母。则此正尤翁所谓无经据。而只以便于世人之承用。遂为不易之定制者也。且违其创制仪式。非盛德则不敢之训也。如何如何。愿更入商量。与俞金城(彦䥧)
客冬。敬修候仪。兼呈司马两榜。而迄未承复。岂洪乔之致耶。即此旱炎。政履何似。本县风土如何。民俗亦如何。牛刀之用。不废于割鸡否。遥想日奉专城之养于两堂。其乐可
白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第 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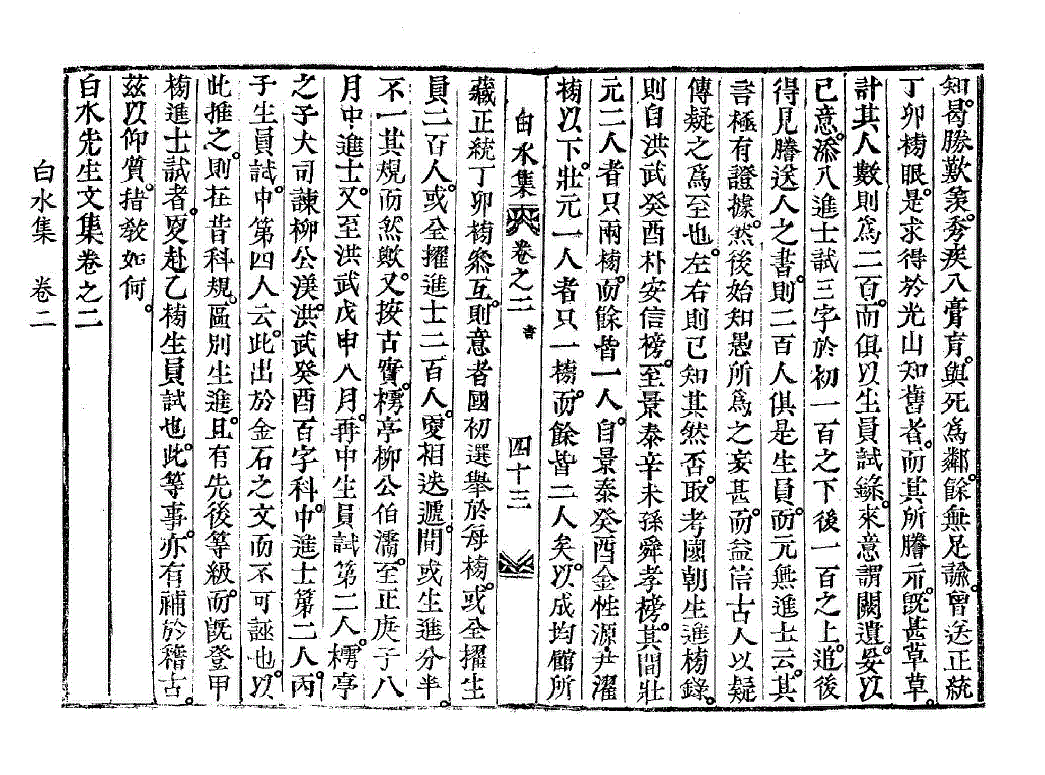 知。曷胜叹羡。秀疾入膏肓。与死为邻。馀无足谕。曾送正统丁卯榜眼。是求得于光山知旧者。而其所誊示。既甚草草。计其人数则为二百。而俱以生员试录。来意谓阙遗。妄以己意。添入进士试三字于初一百之下后一百之上。追后得见誊送人之书。则二百人俱是生员。而元无进士云。其言极有證据。然后始知愚所为之妄甚。而益信古人以疑传疑之为至也。左右则已知其然否。取考国朝生进榜录。则自洪武癸酉朴安信榜。至景泰辛未孙舜孝榜。其间壮元二人者只两榜。而馀皆一人。自景泰癸酉金性源,尹濯榜以下。壮元一人者只一榜。而馀皆二人矣。以成均馆所藏正统丁卯榜参互。则意者国初选举于每榜。或全擢生员二百人。或全擢进士二百人。更相迭递。间或生进分半。不一其规而然欤。又按古实。樗亭柳公伯濡。至正庚子八月中进士。又至洪武戊申八月。再中生员试第二人。樗亭之子大司谏柳公渼。洪武癸酉百字科。中进士第二人。丙子生员试。中第四人云。此出于金石之文而不可诬也。以此推之。则在昔科规。区别生进。且有先后等级。而既登甲榜进士试者。更赴乙榜生员试也。此等事。亦有补于稽古。玆以仰质。指教如何。
知。曷胜叹羡。秀疾入膏肓。与死为邻。馀无足谕。曾送正统丁卯榜眼。是求得于光山知旧者。而其所誊示。既甚草草。计其人数则为二百。而俱以生员试录。来意谓阙遗。妄以己意。添入进士试三字于初一百之下后一百之上。追后得见誊送人之书。则二百人俱是生员。而元无进士云。其言极有證据。然后始知愚所为之妄甚。而益信古人以疑传疑之为至也。左右则已知其然否。取考国朝生进榜录。则自洪武癸酉朴安信榜。至景泰辛未孙舜孝榜。其间壮元二人者只两榜。而馀皆一人。自景泰癸酉金性源,尹濯榜以下。壮元一人者只一榜。而馀皆二人矣。以成均馆所藏正统丁卯榜参互。则意者国初选举于每榜。或全擢生员二百人。或全擢进士二百人。更相迭递。间或生进分半。不一其规而然欤。又按古实。樗亭柳公伯濡。至正庚子八月中进士。又至洪武戊申八月。再中生员试第二人。樗亭之子大司谏柳公渼。洪武癸酉百字科。中进士第二人。丙子生员试。中第四人云。此出于金石之文而不可诬也。以此推之。则在昔科规。区别生进。且有先后等级。而既登甲榜进士试者。更赴乙榜生员试也。此等事。亦有补于稽古。玆以仰质。指教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