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厚庵集卷之六 第 x 页
厚庵集卷之六
序
序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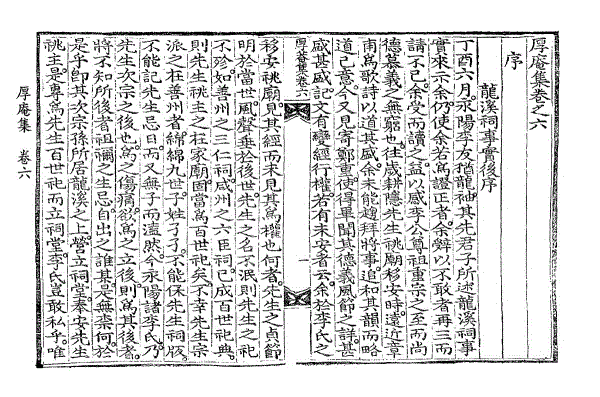 龙溪祠事实后序
龙溪祠事实后序丁酉六月。永阳李友犹龙。袖其先君子所述龙溪祠事实来示余。仍使余若为證正者。余辞以不敢者再三而请不已。余受而读之。益以感李公尊祖重宗之至而尚德慕义之无穷也。往岁耕隐先生祧庙移安时。远近章甫为歌诗以道其盛。余未能趋拜将事。追和其韵而略道己意。今又见寄郑重。使得毕闻其德义风节之详。甚盛甚盛。记文有变经行权。若有未安者云。余于李氏之移安祧庙。见其经而未见其为权也何者。先生之贞节明于当世。风声垂于后世。先生之名不泯则先生之祀不殄。如善州之三仁祠。咸州之六臣祠。已成百世祀典。则先生祧主之在家庙。固当为百世祀矣。不幸先生宗派之在善州者。绵绵九世。子姓孑孑。不能保先生祠版。不能记先生忌日。而又无子而溘然。今永阳诸李氏。乃先生次宗之后也。为之伤痛。欲为之立后。则为其后者。将不知所后者祖祢之生忌。自出之谁某。是无柰何。于是乎即其次宗孙所居龙溪之上。营立祠堂。奉安先生祧主。是专为先生百世祀而立祠堂。李氏岂敢私乎。唯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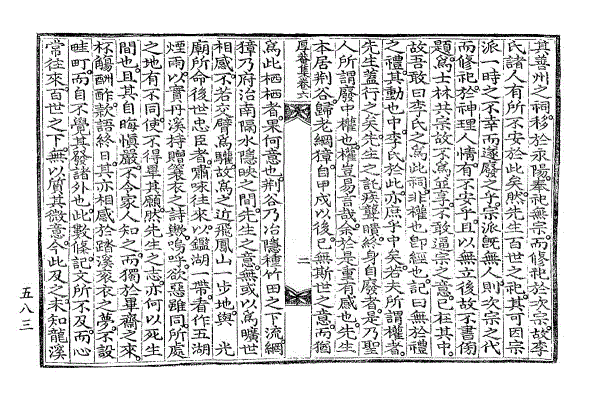 其善州之祠。移于永阳。奉祀无宗。而修祀于次宗。故李氏诸人有所不安于此矣。然先生百世之祀。其可因宗派一时之不幸而遂废之乎。宗派既无人。则次宗之代而修祀。于神理人情。有不安乎。且以无立后故不书傍题。为士林共宗故不为并享。不敢逼宗之意。已在其中。故吾敢曰李氏之为此祠。非权也即经也。记曰无于礼之礼。其动也中。李氏于此。亦庶乎中矣。若夫所谓权者。先生盖行之矣。先生之托疾聋瞆。终身自废者。是乃圣人所谓废中权也。权岂易言哉。余于是重有感也。先生本居荆谷。归老网獐。自甲戌以后。已无斯世之意。而犹为此栖栖者。果何意也。荆谷乃冶隐种竹田之下流。网獐乃府治南隔水隐映之间。先生之意。无或以为旷世相感。不若交臂为驩。故为之近飞凤山一步地。与 光庙所命后世忠臣者。啸咏往来。以鉴湖一带。看作五湖烟雨。以实丹溪持赠蓑衣之诗欤。呜呼。欲恶虽同。所处之地有不同。使不得毕其愿。然先生之志。亦何以死生间也。且其自晦慎严。不令家人知之。而独于毕斋之来。杯觞酬酢。款语终日。其亦相感于踏溪衮衣之梦。不设畦町。而自不觉其发诸外也。此数条。记文所不及。而心常往来。百世之下。无以质其微意。今此及之。未知龙溪
其善州之祠。移于永阳。奉祀无宗。而修祀于次宗。故李氏诸人有所不安于此矣。然先生百世之祀。其可因宗派一时之不幸而遂废之乎。宗派既无人。则次宗之代而修祀。于神理人情。有不安乎。且以无立后故不书傍题。为士林共宗故不为并享。不敢逼宗之意。已在其中。故吾敢曰李氏之为此祠。非权也即经也。记曰无于礼之礼。其动也中。李氏于此。亦庶乎中矣。若夫所谓权者。先生盖行之矣。先生之托疾聋瞆。终身自废者。是乃圣人所谓废中权也。权岂易言哉。余于是重有感也。先生本居荆谷。归老网獐。自甲戌以后。已无斯世之意。而犹为此栖栖者。果何意也。荆谷乃冶隐种竹田之下流。网獐乃府治南隔水隐映之间。先生之意。无或以为旷世相感。不若交臂为驩。故为之近飞凤山一步地。与 光庙所命后世忠臣者。啸咏往来。以鉴湖一带。看作五湖烟雨。以实丹溪持赠蓑衣之诗欤。呜呼。欲恶虽同。所处之地有不同。使不得毕其愿。然先生之志。亦何以死生间也。且其自晦慎严。不令家人知之。而独于毕斋之来。杯觞酬酢。款语终日。其亦相感于踏溪衮衣之梦。不设畦町。而自不觉其发诸外也。此数条。记文所不及。而心常往来。百世之下。无以质其微意。今此及之。未知龙溪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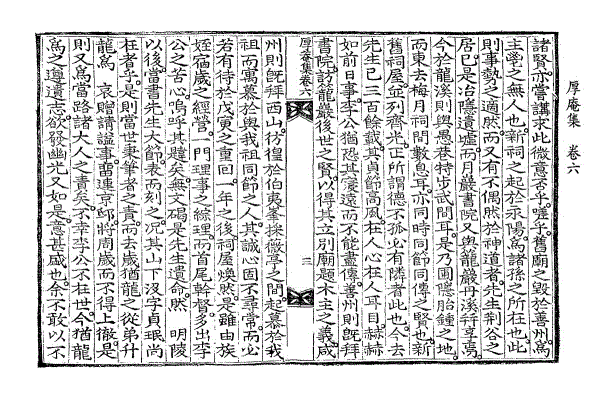 诸贤。亦尝讲求此微意否乎。嗟乎。旧庙之毁于善州。为主鬯之无人也。新祠之起于永阳。为诸孙之所在也。此则事势之适然。而又有不偶然于神道者。先生荆谷之居。已是冶隐遗墟。而月岩书院又与笼岩丹溪并享焉。今于龙溪则与愚巷特步武间耳。是乃圃隐胎钟之地。而东去梅月祠间数息耳。亦同时同节同传之贤也。新旧祠屋。并列齐光。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者此也。今去先生已三百馀载。其贞节高风。在人心在人耳目。赫赫如前日事。李公犹恐其寖远而不能尽传。善州则既拜书院。访笼岩后世之贤。以得其立别庙题木主之义。咸州则既拜西山。彷徨于伯夷峰采薇亭之间。起慕于我祖而寓慕于与我祖同节之人。其诚心固不寻常。而必若有待于戊寅之重回。一年之后。祠屋焕然。是虽由族侄宿岁之经营。一门理事之综理。而首尾干督。多出李公之苦心。呜呼其韪矣。无文碣是先生遗命。然 明陵以后。当书先生大节。表而刻之。况其山下没字贞珉尚在者乎。是则当世秉笔者之责。而去岁犹龙之从弟升龙为 哀赠请谥事。留连京邸。将周岁而不得上彻。是则又为当路诸大人之责矣。不幸李公不在世。今犹龙为之遵遗志。欲发幽光又如是。意甚盛也。余不敢以不
诸贤。亦尝讲求此微意否乎。嗟乎。旧庙之毁于善州。为主鬯之无人也。新祠之起于永阳。为诸孙之所在也。此则事势之适然。而又有不偶然于神道者。先生荆谷之居。已是冶隐遗墟。而月岩书院又与笼岩丹溪并享焉。今于龙溪则与愚巷特步武间耳。是乃圃隐胎钟之地。而东去梅月祠间数息耳。亦同时同节同传之贤也。新旧祠屋。并列齐光。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者此也。今去先生已三百馀载。其贞节高风。在人心在人耳目。赫赫如前日事。李公犹恐其寖远而不能尽传。善州则既拜书院。访笼岩后世之贤。以得其立别庙题木主之义。咸州则既拜西山。彷徨于伯夷峰采薇亭之间。起慕于我祖而寓慕于与我祖同节之人。其诚心固不寻常。而必若有待于戊寅之重回。一年之后。祠屋焕然。是虽由族侄宿岁之经营。一门理事之综理。而首尾干督。多出李公之苦心。呜呼其韪矣。无文碣是先生遗命。然 明陵以后。当书先生大节。表而刻之。况其山下没字贞珉尚在者乎。是则当世秉笔者之责。而去岁犹龙之从弟升龙为 哀赠请谥事。留连京邸。将周岁而不得上彻。是则又为当路诸大人之责矣。不幸李公不在世。今犹龙为之遵遗志。欲发幽光又如是。意甚盛也。余不敢以不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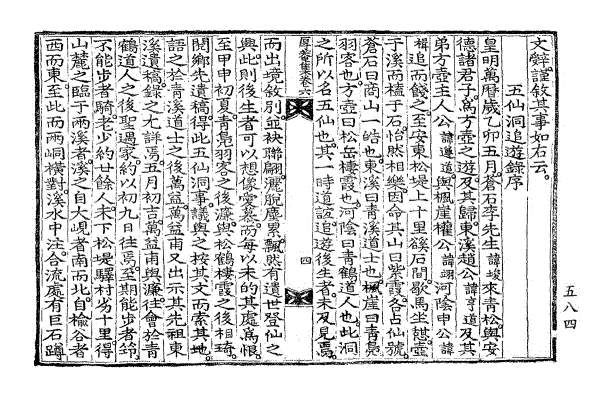 文辞。谨叙其事如右云。
文辞。谨叙其事如右云。五仙洞追游录序
皇明万历岁乙卯五月。苍石李先生(讳埈)来青松。与安德诸君子。为方壶之游。及其归。东溪赵公(讳亨道)及其弟方壶主人公(讳遵道)。与枫崖权公(讳翊)河阴申公(讳楫)追而饯之。至安东松堤上十里溪石间。歇马坐憩。壶于溪而榼于石。怡然相乐。因命其山曰紫霞。各占仙号。苍石曰商山一皓也。东溪曰青溪道士也。枫崖曰青凫羽客也。方壶曰松岳栖霞也。河阴曰青鹤道人也。此洞之所以名五仙也。其一时道谊。追游后生者。未及见焉。而出境叙别。并袂联翩。洒脱尘累。飘然有遗世登仙之兴。此则后生者可以想像爱慕。而每以未的其处为恨。至甲申初夏。青凫羽客之后濂。与松鹤栖霞之后相琦。阅乡先遗稿。得此五仙洞事。议与之按其文而索其地。语之于青溪道士之后万益。万益甫又出示其先祖东溪遗稿。录之尤详焉。五月初吉。万益甫与濂。往会于青鹤道人之后圣遇家。约以初九日往焉。至期能步者筇。不能步者骑。老少约廿馀人。未下松堤驿村劣十里。得山麓之临于两溪者。溪之自大岘者南而北。自榆谷者西而东。至此而两峒横对。溪水中注。合流处有巨石蹲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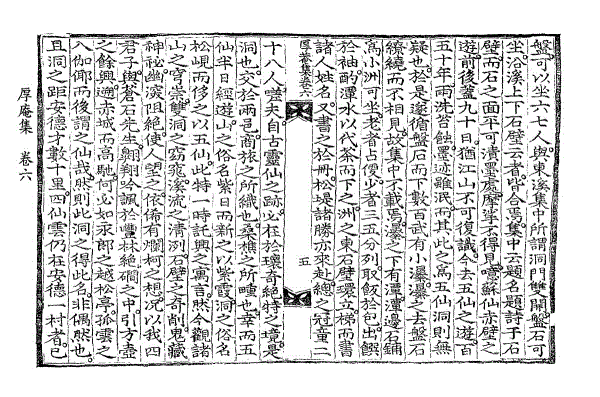 盘。可以坐六七人。与东溪集中所谓洞门双开。盘石可坐。沿溪上下石壁云者。皆合焉。集中云题名题诗于石壁。而石之面平可渍墨处。摩挲不得见。噫苏仙赤壁之游。前后盖九十日。犹江山不可复识。今去五仙之游。百五十年。雨洗苔蚀。墨迹虽泯。而其此之为五仙洞则无疑也。于是遂循盘石而下数百武有小瀑。瀑之去盘石缭绕而不相见。故集中不载焉。瀑之下有潭。潭边石铺为小洲可坐。老者占便。少者三五分列。取饭于包。出馔于袖。酌潭水以代茶而下之。洲之东石壁环立。梯而书诸人姓名。又书之于册。松堤诸胜亦来赴。总之冠童二十八人。嗟夫。自古灵仙之迹。必在于瑰奇绝特之境。是洞也。交于两邑。商旅之所织也。桑樵之所疃也。幸而五仙半日经游。山之俗名紫日而新之以紫霞。洞之俗名松岘而侈之以五仙。此特一时托兴之寓言。然今观诸山之穹崇。双洞之窈窕。溪流之清洌。石壁之奇削。鬼藏神秘。幽深阻绝。使人望之。依俙有烂柯之想。况以我四君子。与苍石先生。翱翔吟讽于丰林绝涧之中。引方壶之馀兴。溯赤城而高驰。何必如永郎之越松亭。孤云之入伽倻而后谓之仙哉。然则此洞之得此名。非偶然也。且洞之距安德才数十里。四仙云仍在安德一村者。已
盘。可以坐六七人。与东溪集中所谓洞门双开。盘石可坐。沿溪上下石壁云者。皆合焉。集中云题名题诗于石壁。而石之面平可渍墨处。摩挲不得见。噫苏仙赤壁之游。前后盖九十日。犹江山不可复识。今去五仙之游。百五十年。雨洗苔蚀。墨迹虽泯。而其此之为五仙洞则无疑也。于是遂循盘石而下数百武有小瀑。瀑之去盘石缭绕而不相见。故集中不载焉。瀑之下有潭。潭边石铺为小洲可坐。老者占便。少者三五分列。取饭于包。出馔于袖。酌潭水以代茶而下之。洲之东石壁环立。梯而书诸人姓名。又书之于册。松堤诸胜亦来赴。总之冠童二十八人。嗟夫。自古灵仙之迹。必在于瑰奇绝特之境。是洞也。交于两邑。商旅之所织也。桑樵之所疃也。幸而五仙半日经游。山之俗名紫日而新之以紫霞。洞之俗名松岘而侈之以五仙。此特一时托兴之寓言。然今观诸山之穹崇。双洞之窈窕。溪流之清洌。石壁之奇削。鬼藏神秘。幽深阻绝。使人望之。依俙有烂柯之想。况以我四君子。与苍石先生。翱翔吟讽于丰林绝涧之中。引方壶之馀兴。溯赤城而高驰。何必如永郎之越松亭。孤云之入伽倻而后谓之仙哉。然则此洞之得此名。非偶然也。且洞之距安德才数十里。四仙云仍在安德一村者。已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5L 页
 六七世。亦能保刘氏鸡犬于南阡北陌之间。约日来会。又得天中之节。此则尤不为偶然也。溪山不改。节物依然。而五仙之上为真仙。又皆百馀年矣。徘徊踯躅。自然有循旧念先之感。是何自在仙区。亦为人怆心之地也邪。于其将散也。皆曰此会不可今年已也。又不必五月。每年红绿。便步来会。使此洞之名不泯。则五仙之迹不晦。而远近好古之君子。亦将有指而言之而广其传也。惜乎。商山远在数百里外。苍老后世之贤。不得与之同此会而同此怀也。万益甫首为之次苍老韵。以次续和。濂又敢叙其事而书之于册之末。
六七世。亦能保刘氏鸡犬于南阡北陌之间。约日来会。又得天中之节。此则尤不为偶然也。溪山不改。节物依然。而五仙之上为真仙。又皆百馀年矣。徘徊踯躅。自然有循旧念先之感。是何自在仙区。亦为人怆心之地也邪。于其将散也。皆曰此会不可今年已也。又不必五月。每年红绿。便步来会。使此洞之名不泯。则五仙之迹不晦。而远近好古之君子。亦将有指而言之而广其传也。惜乎。商山远在数百里外。苍老后世之贤。不得与之同此会而同此怀也。万益甫首为之次苍老韵。以次续和。濂又敢叙其事而书之于册之末。藏庵续游录诗序
中山诸胜。当以万景台白玉峰为最而庵间焉。始庵主令公(黄翼再)从先垄筑室于白华山之东。与白玉峰相直。因山名而寓笙诗孝子之义。扁其斋曰白华。既又构此庵于万景台之前。洞天寥旷。岩麓峭茜。乃隐者所盘旋。而自题曰藏庵。盖公有意于敛藏自修。为兴公遂初地也。是岁之日南至。余以事来中山。公族子二上舍丈导余游焉。于是焉上玉峰顶。俯瞰白华斋轩。缵叟甫左右眄而指示其所谓十景者。步而下。上洗心石。即所谓漏十景而冠十景者。乃密庵所名以二字也。夜张灯酒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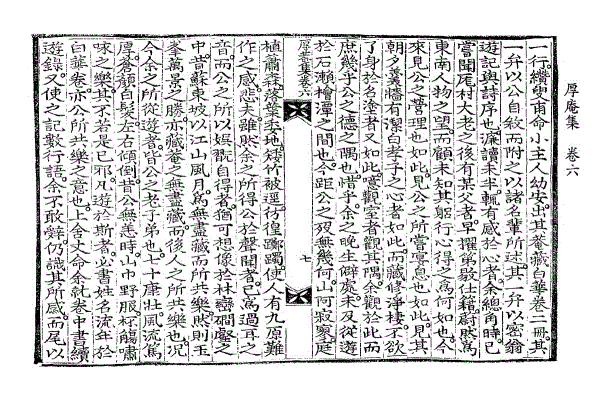 一行。缵叟甫命小主人幼安。出其庵藏白华卷二册。其一弁以公自叙而附之以诸名辈所述。其一弁以密翁游记与诗序也。濂读未半。辄有感于心者。余总角时。已尝闻厖村大老之后有某父者。早擢第扬仕籍。蔚然为东南人物之望。而顾未知其躬行心得之为何如也。今来见公之营理也如此。见公之所尝宴息也如此。见其朝夕羹墙有洁白孝子之心者如此。而藏修净栖。不欲了身于名涂者又如此。噫观室者观其隅。余观于此而庶几乎公之德之隅也。惜乎。余之晚生僻处。未及从游于石濑桧潭之间也。今距公之殁无几何。山阿寂寥。庭植萧森。落叶委地。矮竹被径。彷徨踯躅。使人有九原难作之感。悲夫。虽然余之所得公于声闻者。已为过耳之音。而公之所以娱玩自得者。犹可想像于林峦涧壑之中。昔苏东坡以江山风月。为无尽藏而所共乐。然则玉峰万景之胜。亦藏庵之无尽藏。而后人之所共乐也。况今余之所从游者。皆公之老子弟也。七十康壮。风流笃厚。苍颜白发。左右倾倒。昔公无恙时。山巾野服。杯觞啸咏之乐。其不若是已邪。凡游于斯者。必书姓名流年于白华卷。亦公所共乐之意也。上舍丈命余就卷中书续游录。又使之记数行语。余不敢辞。仍识其所感。而尾以
一行。缵叟甫命小主人幼安。出其庵藏白华卷二册。其一弁以公自叙而附之以诸名辈所述。其一弁以密翁游记与诗序也。濂读未半。辄有感于心者。余总角时。已尝闻厖村大老之后有某父者。早擢第扬仕籍。蔚然为东南人物之望。而顾未知其躬行心得之为何如也。今来见公之营理也如此。见公之所尝宴息也如此。见其朝夕羹墙有洁白孝子之心者如此。而藏修净栖。不欲了身于名涂者又如此。噫观室者观其隅。余观于此而庶几乎公之德之隅也。惜乎。余之晚生僻处。未及从游于石濑桧潭之间也。今距公之殁无几何。山阿寂寥。庭植萧森。落叶委地。矮竹被径。彷徨踯躅。使人有九原难作之感。悲夫。虽然余之所得公于声闻者。已为过耳之音。而公之所以娱玩自得者。犹可想像于林峦涧壑之中。昔苏东坡以江山风月。为无尽藏而所共乐。然则玉峰万景之胜。亦藏庵之无尽藏。而后人之所共乐也。况今余之所从游者。皆公之老子弟也。七十康壮。风流笃厚。苍颜白发。左右倾倒。昔公无恙时。山巾野服。杯觞啸咏之乐。其不若是已邪。凡游于斯者。必书姓名流年于白华卷。亦公所共乐之意也。上舍丈命余就卷中书续游录。又使之记数行语。余不敢辞。仍识其所感。而尾以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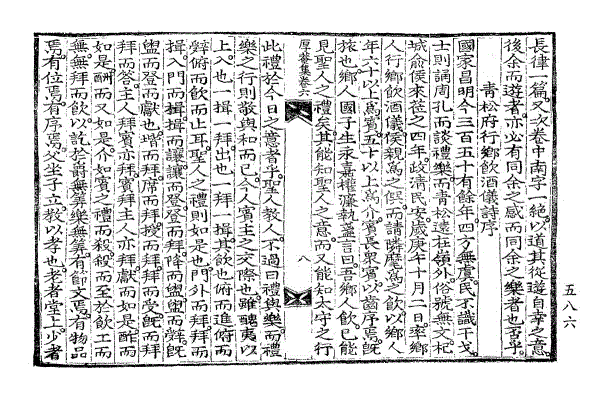 长律一篇。又次卷中南字一绝。以道其从游自幸之意。后余而游者。亦必有同余之感而同余之乐者也否乎。
长律一篇。又次卷中南字一绝。以道其从游自幸之意。后余而游者。亦必有同余之感而同余之乐者也否乎。青松府行乡饮酒仪诗序
国家昌明今三百五十有馀年。四方无虞。民不识干戈。士则诵周孔而谈礼乐。而青松远在岭外。俗号无文。杞城俞侯来莅之四年。政清民安。岁庚午十月二日。率乡人行乡饮酒仪。侯亲为之僎。而请邻麾为之饮。以乡人年六十以上为宾。五十以上为介。宾长众宾。以齿序焉。既旅也。乡人国子生永嘉权濂执盏言曰。吾乡人饮。已能见圣人之礼矣。其能知圣人之意。而又能知太守之行此礼于今日之意者乎。圣人教人。不过曰礼与乐。而礼乐之行则敬与和而已。今人宾主之交际也。虽丑夷以上。入也一揖一拜。出也一拜一揖。其饮也俯而进俯而辞俯而饮而止耳。圣人之礼则如是也。门外而拜。拜而揖。入门而揖。揖而让。让而登。登而拜。降而盥。盥而辞。既盥而登而献也。阶而拜。席而拜。授而拜。拜而受。既而拜拜而答。主人拜宾亦拜。宾拜主人亦拜。献而如是。酢而如是。酬而又如是。介如宾之礼而杀。杀而至于饮工而无。无拜而饮。以讫于爵无算乐无算。有节文焉。有物品焉。有位焉。有序焉。父坐子立。教以孝也。老者堂上。少者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7H 页
 堂下。教以悌也。歌鹿鸣。教以和朋友也。歌二南。教以正家也。僎东而笙堂下。所以辨贵贱也。鼎俎盏斝之间。人伦备焉。此圣人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而息陵犯争讼之风者也。此礼之废久矣。今我侯承 国朝化民之意。行之一乡。以试古人牛刀之戏。而使人油然有孝弟之心。薾然销觕厉之气。使青松一区。变而为退逊士君子之乡。其意甚盛矣。而不知太史氏书之策曰青松倅某以 国家行乡饮酒仪。以善其风俗也否乎。行于乡。不若行于国为广且大焉。既以诵于侯。又以望于 王庭之君子也。
堂下。教以悌也。歌鹿鸣。教以和朋友也。歌二南。教以正家也。僎东而笙堂下。所以辨贵贱也。鼎俎盏斝之间。人伦备焉。此圣人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而息陵犯争讼之风者也。此礼之废久矣。今我侯承 国朝化民之意。行之一乡。以试古人牛刀之戏。而使人油然有孝弟之心。薾然销觕厉之气。使青松一区。变而为退逊士君子之乡。其意甚盛矣。而不知太史氏书之策曰青松倅某以 国家行乡饮酒仪。以善其风俗也否乎。行于乡。不若行于国为广且大焉。既以诵于侯。又以望于 王庭之君子也。寿勋冠席。次一郎寿夏诗序。
余年三十五始举汝。汝今十七而冠。余窭矣。不能具礼币请宾友。以毕行三加之仪。然为父望成于子之心。固在于今日。名曰寿勋而字之曰钦徵。寿尧之所辞而敢以是称之者。尧十六以唐侯为天子。宅帝位百年。盖其钦明之德。验于外者悠久。而传所称大德必受命者是也。今去帝尧四千年有馀矣。云日之表。恭让之德。不可得以见。而又不可得以名矣。虽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岂欺我哉。惟天降衷。固无古今之异。而圣狂之别。亶不外于钦与不钦。此帝典第一义。所以蔽之曰钦明而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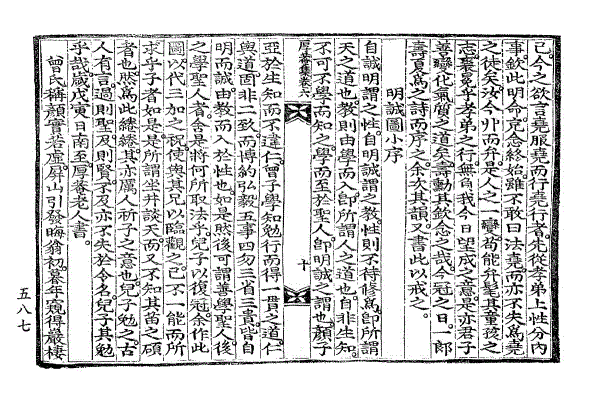 已。今之欲言尧服尧而行尧行者。先从孝弟上性分内事。钦此明命。克念终始。虽不敢曰法尧。而亦不失为尧之徒矣。汝今丱而弁。是人之一变。苟能弁髦其童孩之志。裘冕乎孝弟之行。无负我今日望成之意。是亦君子善变化气质之道矣。寿勋其钦念之哉。今冠之日。一郎寿夏为之诗而序之。余次其韵。又书此以戒之。
已。今之欲言尧服尧而行尧行者。先从孝弟上性分内事。钦此明命。克念终始。虽不敢曰法尧。而亦不失为尧之徒矣。汝今丱而弁。是人之一变。苟能弁髦其童孩之志。裘冕乎孝弟之行。无负我今日望成之意。是亦君子善变化气质之道矣。寿勋其钦念之哉。今冠之日。一郎寿夏为之诗而序之。余次其韵。又书此以戒之。明诚图小序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性则不待修为。即所谓天之道也。教则由学而入。即所谓人之道也。自非生知。不可不学而知之。学而至于圣人。即明诚之谓也。颜子亚于生知而不违仁。曾子学知勉行而得一贯之道。仁与道。固非二致。而博约弘毅五事四勿三省三贵。皆自明而诚。由教而入于性也。如是然后可谓善学圣人。后之学圣人者。舍是将何所取法乎。儿子以复冠。余作此图。以代三加之祝。使与其兄以临观之。己不一能而所求乎子者如是。是所谓坐井谈天。而又不知其苗之硕者也。然为此绻绻。其亦厉人祈子之意也。儿子勉之。古人有言。过则圣。及则贤。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儿子其勉乎哉。岁戊寅日南至。厚庵老人书。
曾氏称颜实若虚。屏山引发晦翁初。暮年窥得岩栖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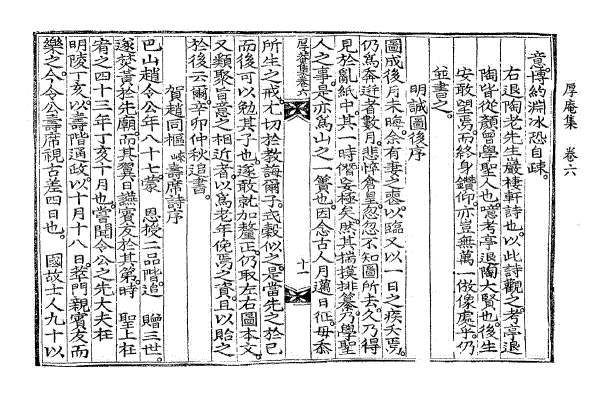 意。博约渊冰恐自疏。
意。博约渊冰恐自疏。右退陶老先生岩栖轩诗也。以此诗观之。考亭退陶皆从颜曾学圣人也。噫考亭退陶大贤也。后生安敢望焉。而终身钻仰。亦岂无万一仿像处乎。仍并书之。
明诚图后序
图成后月未晦。余有妻之丧。以临又以一日之疾夭焉。仍为奔迸者数月。悲悴仓皇。忽忽不知图所去。久乃得见于乱纸中。其一时僭妄极矣。然其揣摸排纂。乃学圣人之事。是亦为山之一篑也。因念古人月迈日征。毋忝所生之戒。尤切于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是当先之于己而后可以勉其子也。遂敢就加釐正。仍取左右图本文。又类聚旨意之相近者。以为老年俛焉之资。且以贻之于后云尔。辛卯仲秋追书。
贺赵同枢(崃)寿席诗序
巴山赵令公年八十七。蒙 恩授二品阶。追 赠三世。遂焚黄于先庙。而其翼日宴宾友于其第。时 圣上在宥之四十三年丁亥十月也。尝闻令公之先大夫在 明陵丁亥。以寿阶通政。以十月十八日。萃门亲宾友而乐之。今令公寿席视古差四日也。 国故士人九十以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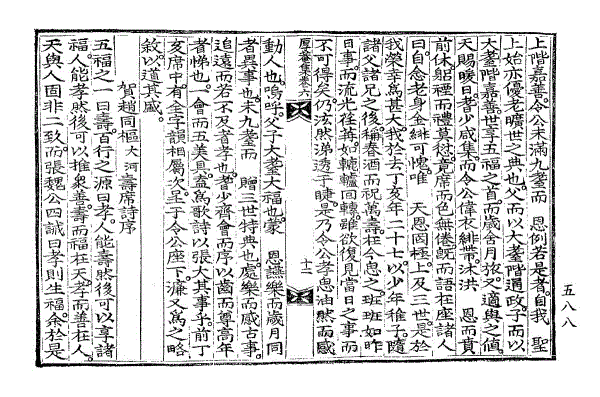 上阶嘉善。令公未满九耋而 恩例若是者。自我 圣上始亦优老旷世之典也。父而以大耋阶通政。子而以大耋阶嘉善。世享五福之首。而岁舍月旅。又适与之值。天赐暖日。耆少咸集。而令公伟衣绯带。沐洪 恩而贲前休。躬禋而礼莫愆。竟席而色无倦。既而语在座诸人曰。自念老身金绯可愧。唯 天恩罔极。上及三世。是于我荣幸为甚大。我于去丁亥年二十七。以少年稚子。随诸父诸兄之后。称春酒而祝万寿。在今思之。班班如昨日事。而流光荏苒。如辘轳回转。虽欲复见当日之事而不可得矣。仍泫然涕透于睫。是乃令公孝思油然而感动人也。呜呼。父子大耋大福也。蒙 恩宴乐而岁月同者异事也。未九耋而 赠三世特典也。处乐而感古事。追远而若不及者孝也。耆少齐会而序以齿而尊高年者悌也。一会而五美具。盍为歌诗以张大其事乎。前丁亥席中。有全字韵相属次。呈于令公座下。濂又为之略叙。以道其盛。
上阶嘉善。令公未满九耋而 恩例若是者。自我 圣上始亦优老旷世之典也。父而以大耋阶通政。子而以大耋阶嘉善。世享五福之首。而岁舍月旅。又适与之值。天赐暖日。耆少咸集。而令公伟衣绯带。沐洪 恩而贲前休。躬禋而礼莫愆。竟席而色无倦。既而语在座诸人曰。自念老身金绯可愧。唯 天恩罔极。上及三世。是于我荣幸为甚大。我于去丁亥年二十七。以少年稚子。随诸父诸兄之后。称春酒而祝万寿。在今思之。班班如昨日事。而流光荏苒。如辘轳回转。虽欲复见当日之事而不可得矣。仍泫然涕透于睫。是乃令公孝思油然而感动人也。呜呼。父子大耋大福也。蒙 恩宴乐而岁月同者异事也。未九耋而 赠三世特典也。处乐而感古事。追远而若不及者孝也。耆少齐会而序以齿而尊高年者悌也。一会而五美具。盍为歌诗以张大其事乎。前丁亥席中。有全字韵相属次。呈于令公座下。濂又为之略叙。以道其盛。贺赵同枢(大河)寿席诗序
五福之一曰寿。百行之源曰孝。人能寿然后可以享诸福。人能孝然后可以推众善。寿而福在天。孝而善在人。天与人固非二致。而张魏公四诫曰孝则生福。余于是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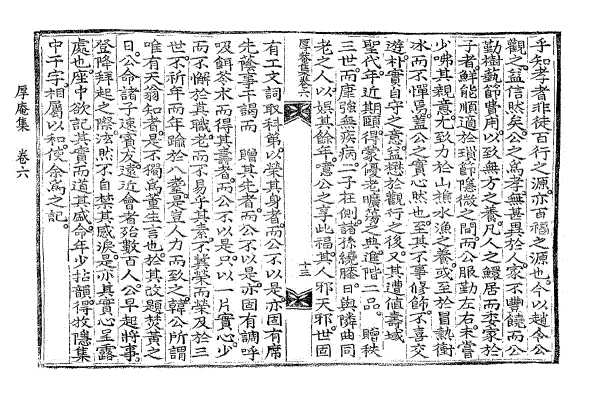 乎知孝者非徒百行之源。亦百福之源也。今以赵令公观之。益信然矣。公之为孝。无甚异于人。家不丰饶而公勤树蓺节费用。以致无方之养。凡人之鳏居而委家于子者。鲜能顺适于琐节隐微之间。而公服勤左右。未尝少咈其亲意。尤致力于山樵水渔之养。或至于冒热冲冰而不惮焉。盖公之实心然也。至其不事修饰。不喜交游。朴实自守之意。益懋于观行之后。又其遭值寿域 圣代。年近期颐。得蒙优老旷荡之典。进阶二品。 赠秩三世。而康强无疾病。二子在侧。诸孙绕膝。日与邻曲同老之人。以娱其馀年。噫公之享此福。其人邪天邪。世固有工文词取科第。以荣其身者。而公不以是。亦固有席先荫事干谒而 赠其先者。而公不以是。亦固有调呼吸饵苓朮而得其寿者。而公不以是。只以一片实心。少而不懈于其职。老而不易乎其素。不冀荣而荣及于三世。不祈年而年踰于八耋。是岂人力而致之。韩公所谓唯有天翁知者。是不独为董生言也。于其改题焚黄之日。公命诸子速宾友。远近会者殆数百人。公早起将事。登降拜起之际。泫然不自禁其感泪。是亦其实心呈露处也。座中欲记其实而道其盛。命年少拈韵。得牧隐集中干字。相属以和。使余为之记。
乎知孝者非徒百行之源。亦百福之源也。今以赵令公观之。益信然矣。公之为孝。无甚异于人。家不丰饶而公勤树蓺节费用。以致无方之养。凡人之鳏居而委家于子者。鲜能顺适于琐节隐微之间。而公服勤左右。未尝少咈其亲意。尤致力于山樵水渔之养。或至于冒热冲冰而不惮焉。盖公之实心然也。至其不事修饰。不喜交游。朴实自守之意。益懋于观行之后。又其遭值寿域 圣代。年近期颐。得蒙优老旷荡之典。进阶二品。 赠秩三世。而康强无疾病。二子在侧。诸孙绕膝。日与邻曲同老之人。以娱其馀年。噫公之享此福。其人邪天邪。世固有工文词取科第。以荣其身者。而公不以是。亦固有席先荫事干谒而 赠其先者。而公不以是。亦固有调呼吸饵苓朮而得其寿者。而公不以是。只以一片实心。少而不懈于其职。老而不易乎其素。不冀荣而荣及于三世。不祈年而年踰于八耋。是岂人力而致之。韩公所谓唯有天翁知者。是不独为董生言也。于其改题焚黄之日。公命诸子速宾友。远近会者殆数百人。公早起将事。登降拜起之际。泫然不自禁其感泪。是亦其实心呈露处也。座中欲记其实而道其盛。命年少拈韵。得牧隐集中干字。相属以和。使余为之记。厚庵集卷之六 第 58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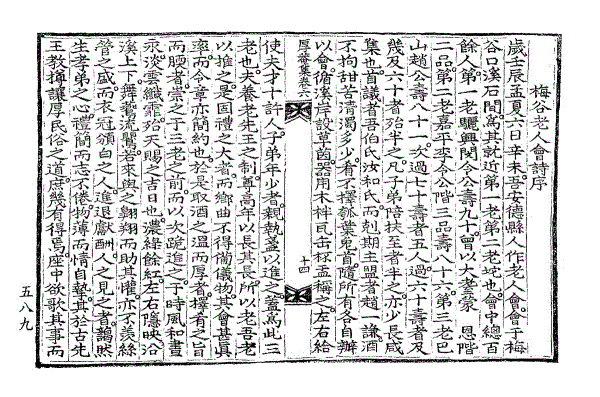 梅谷老人会诗序
梅谷老人会诗序岁壬辰孟夏六日辛未。吾安德县人作老人会。会于梅谷口溪石间。为其就近第一老第二老坨也。会中总百馀人。第一老骊兴闵令公寿九十。曾以大耋蒙 恩阶二品。第二老嘉平李令公阶三品寿八十六。第三老巴山赵公寿八十一。次过七十寿者五人。过六十寿者及几及六十者殆半之。凡子弟陪扶至者半之。亦少长咸集也。首议者吾伯氏汝和氏。而剋期主盟者赵一谦。酒不拘甜苦清浊多少。肴不择瓠叶兔首。随所有各自办以会。循溪岸设草茵。器用木柈瓦缶杯盂称之。左右给使夫才十许人。子弟年少者。亲执盏以进之。盖为此三老也。夫养老先王之制。尊高年以长其长。所以老吾老以推之。是固礼之大者。而乡曲不得备仪物。其会甚真率。而令章亦简约也。于是取酒之温而厚者。择肴之旨而腝者。崇之于三老之前。而以次跪进之。于时风和昼永。淡云纤霏。殆天赐之吉日也。浓绿馀红。左右隐映。沿溪上下。舞燕流莺。若来与之翱翔而助其欢。亦不羡丝管之盛。而衣冠颁白之人。进退献酬。人之见之者。蔼然生孝弟之心。礼简而志不倦。物薄而情自挚。其于古先王教撙让厚民俗之道。庶几有得焉。座中欲歌其事而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0H 页
 久其传。使濂为之序。物品之不择精粗。乃今日主盟之令。如余荒拙之辞。亦何敢辞。于是录此。以附于列叙时人之末。且继之以一律焉。
久其传。使濂为之序。物品之不择精粗。乃今日主盟之令。如余荒拙之辞。亦何敢辞。于是录此。以附于列叙时人之末。且继之以一律焉。厚庵集卷之六
记
龟岩书堂记
松。山郡也。其东南诸山。自周王南驰而北折。环抱将六七十里。马坪最居抱之中。夫周王山为山南选胜。而坪之居。与周王对值。是其山水之所合匝。精英之所钟毓。尚或有嵬峨杰特之士作。以符地灵人杰之称。而盖罕有闻焉。此则松之人所共疑且叹者也。 明陵丙戌春。坪之长少相与谋曰凡吾洞无学舍故无学子。无学子故无闻人。盍为置一书塾。于是醵财合力不数年。先营庖舍于新迁。青乌家以吉凶挠之。时亦屡屈。迄十馀岁未克置讲堂矣。 上之壬戌。始贸瓦甋鸠栋材。先竖书堂于坪之南麓。且将移新迁之庖而就之。其抛梁。父老会而祝之。祝之以兴作学士也。堂凡若干楹。合而扁之曰龟岩书堂。永嘉权濂尝过而游焉。坪之长老徐公某父(汉俊)使为之记。濂谢不敢。因进而言曰吾之经游此屡矣。山固崒然而已。水固奫然而已。东西岩麓之胜。朝夕烟云之态。固环植而相羊而已。而今而登焉。山若益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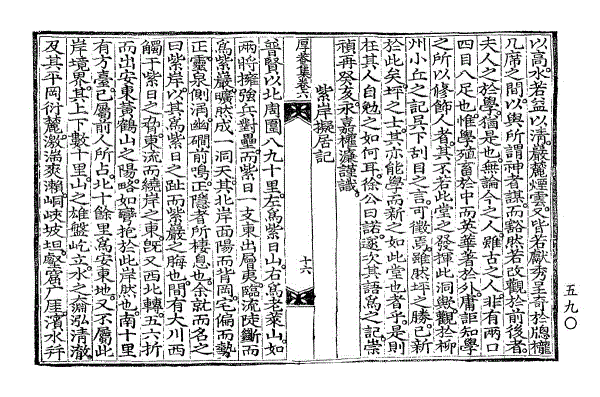 以高。水若益以清。岩麓烟云。又皆若献秀呈奇于窗栊几席之间。以与所谓神者谋。而豁然若改观于前后者。夫人之于学。犹是也。无论今之人。虽古之人。非有两口四目八足也。惟学殖畜于中而英华著于外。庸讵知学之所以修饰人者。其不若此堂之发挥此洞欤。观于柳州小丘之记吴下刮目之言。可徵焉。虽然坪之胜。已新于此矣。坪之士。其亦能学而新之如此堂也者乎。是则在其人自勉之如何耳。徐公曰诺。遂次其语为之记。崇祯再癸亥。永嘉权濂谨识。
以高。水若益以清。岩麓烟云。又皆若献秀呈奇于窗栊几席之间。以与所谓神者谋。而豁然若改观于前后者。夫人之于学。犹是也。无论今之人。虽古之人。非有两口四目八足也。惟学殖畜于中而英华著于外。庸讵知学之所以修饰人者。其不若此堂之发挥此洞欤。观于柳州小丘之记吴下刮目之言。可徵焉。虽然坪之胜。已新于此矣。坪之士。其亦能学而新之如此堂也者乎。是则在其人自勉之如何耳。徐公曰诺。遂次其语为之记。崇祯再癸亥。永嘉权濂谨识。紫岸拟居记
普贤以北周围八九十里。左为紫日山。右为老莱山。如两将拥强兵对垒。而紫日一支东出层夷。临流陡断而为紫岩。旷然成一洞天。其北岸面阳而背冈。宅偏而势正。灵泉侧涌。幽涧前鸣。正隐者所栖息也。余就而名之曰紫岸。以其为紫日之趾而紫岩之脢也。间有大川西触于紫日之胁。东流而绕岸之东。既又西北转。五六折而出安东黄鹤山之阳。略如弯抱于此岸然也。南十里有方台。已属前人所占。北十馀里为安东地。又不属此岸境界。其上下数十里。山之雄盘屹立。水之奫泓清澈。及其平冈衍麓。激湍爽濑。峒峡坡坦。壑窟广厓。滨水并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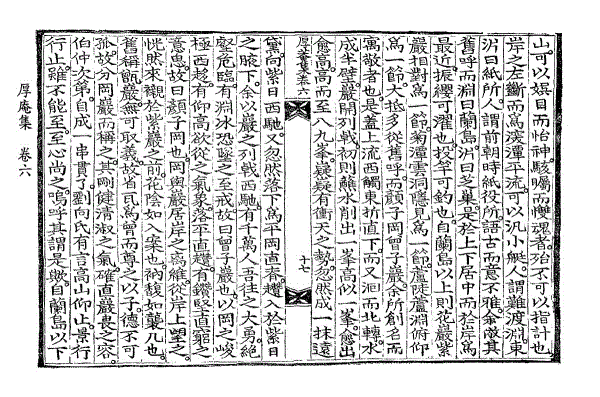 山。可以娱目而怡神。骇瞩而𢥠魂者。殆不可以指计也。岸之左断而为深潭平流。可以汎小艇。人谓难渡渊。东沜曰纸所。人谓前朝时纸役所。语古而意不雅。余仿其旧呼而渊曰兰岛。沜曰芝巢。是于上下居中而于岸为最近。振缨可濯也。投竿可钓也。自兰岛以上则花岩紫岩相对为一节。菊潭云洞隐见为一节。芦陡芦渊俯仰为一节。大抵多从旧呼。而颜子冈曾子岩。余所创名而寓敬者也。是盖上流西触东折直下。而又洄而北转。水成半壁。岩开列戟。初则蘸水削出一峰高似一峰。愈出愈高。高而至八九峰。嶷嶷有冲天之势。忽然成一抹远黛。向紫日西驰。又忽然落下为平冈直脊。趱入于紫日之腋下。余以岩之列戟西驰。有千万人吾往之大勇。绝壑危临。有渊冰恐坠之至戒。故曰曾子岩也。以冈之峻极西趍。有仰高欲从之气象。落平直趱。有钻坚直穷之意思。故曰颜子冈也。冈与岩居岸之离维。从岸上望之。恍然来衬于紫岩之前。花阴如入案也。衲馥如袭几也。旧称甑岩。无可取义。故省瓦为曾而尊之以子。德不可孤。故分冈岩而称之。其刚健清淑之气。确直岩畏之容。伯仲次第。自成一串贯了。刘向氏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至心尚之。呜呼其谓是欤。自兰岛以下
山。可以娱目而怡神。骇瞩而𢥠魂者。殆不可以指计也。岸之左断而为深潭平流。可以汎小艇。人谓难渡渊。东沜曰纸所。人谓前朝时纸役所。语古而意不雅。余仿其旧呼而渊曰兰岛。沜曰芝巢。是于上下居中而于岸为最近。振缨可濯也。投竿可钓也。自兰岛以上则花岩紫岩相对为一节。菊潭云洞隐见为一节。芦陡芦渊俯仰为一节。大抵多从旧呼。而颜子冈曾子岩。余所创名而寓敬者也。是盖上流西触东折直下。而又洄而北转。水成半壁。岩开列戟。初则蘸水削出一峰高似一峰。愈出愈高。高而至八九峰。嶷嶷有冲天之势。忽然成一抹远黛。向紫日西驰。又忽然落下为平冈直脊。趱入于紫日之腋下。余以岩之列戟西驰。有千万人吾往之大勇。绝壑危临。有渊冰恐坠之至戒。故曰曾子岩也。以冈之峻极西趍。有仰高欲从之气象。落平直趱。有钻坚直穷之意思。故曰颜子冈也。冈与岩居岸之离维。从岸上望之。恍然来衬于紫岩之前。花阴如入案也。衲馥如袭几也。旧称甑岩。无可取义。故省瓦为曾而尊之以子。德不可孤。故分冈岩而称之。其刚健清淑之气。确直岩畏之容。伯仲次第。自成一串贯了。刘向氏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至心尚之。呜呼其谓是欤。自兰岛以下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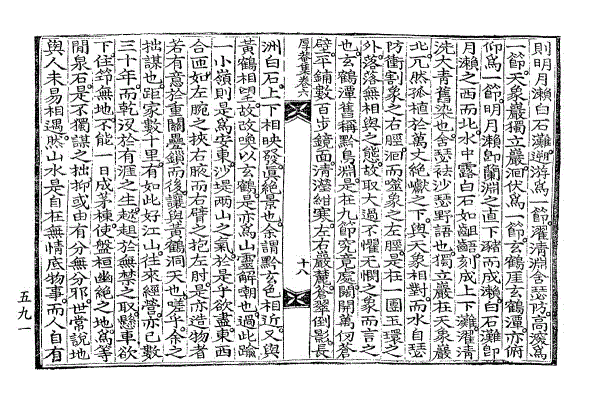 则明月濑白石滩。溯游为一节。濯清渊舍瑟防。高深为一节。天象岩独立岩。洄伏为一节。玄鹤厓玄鹤潭。亦俯仰为一节。明月濑即兰渊之直下潴而成濑。白石滩即月濑之西而北。水中露白石如龃龉。刻成上下滩。濯清洗大青旧染也。舍瑟祛沙瑟野语也。独立岩在天象岩北。兀然孤植于万丈绝巘之下。与天象相对。而水自瑟防冲割象之右胫。洄而噬象之左胫。是在一团玉环之外。落落无相与之态。故取大过不惧无悯之象而言之也。玄鹤潭旧称黔鸟渊。是在九节究竟处。阔开万仞苍壁。平铺数百步镜面。清滢绀寒。左右岩麓。苍翠倒影。长洲白石。上下相映发。真绝景也。余谓黔玄色相近。又与黄鹤相望。故改唤以玄鹤。是亦为山灵解嘲也。过此踰一小岭则是为安东。沙堤两山之气。于是乎欲尽。东西合匝。如左腕之挟右腋而右臂之抱左肘。是亦造物者若有意于重关叠锁而后。让与黄鹤洞天也。嗟乎。余之拙谋也。距家数十里。有如此好江山。往来经营。亦已数三十年。而乾没于有涯之生。趑趄于无禁之取。悬车欲下。住筇无地。不能一日成茅栋。使盘桓幽绝之地。为等閒泉石。是不独谋之拙。抑或由有分无分邪。世常说地与人未易相遇。然山水是自在无情底物事。而人自有
则明月濑白石滩。溯游为一节。濯清渊舍瑟防。高深为一节。天象岩独立岩。洄伏为一节。玄鹤厓玄鹤潭。亦俯仰为一节。明月濑即兰渊之直下潴而成濑。白石滩即月濑之西而北。水中露白石如龃龉。刻成上下滩。濯清洗大青旧染也。舍瑟祛沙瑟野语也。独立岩在天象岩北。兀然孤植于万丈绝巘之下。与天象相对。而水自瑟防冲割象之右胫。洄而噬象之左胫。是在一团玉环之外。落落无相与之态。故取大过不惧无悯之象而言之也。玄鹤潭旧称黔鸟渊。是在九节究竟处。阔开万仞苍壁。平铺数百步镜面。清滢绀寒。左右岩麓。苍翠倒影。长洲白石。上下相映发。真绝景也。余谓黔玄色相近。又与黄鹤相望。故改唤以玄鹤。是亦为山灵解嘲也。过此踰一小岭则是为安东。沙堤两山之气。于是乎欲尽。东西合匝。如左腕之挟右腋而右臂之抱左肘。是亦造物者若有意于重关叠锁而后。让与黄鹤洞天也。嗟乎。余之拙谋也。距家数十里。有如此好江山。往来经营。亦已数三十年。而乾没于有涯之生。趑趄于无禁之取。悬车欲下。住筇无地。不能一日成茅栋。使盘桓幽绝之地。为等閒泉石。是不独谋之拙。抑或由有分无分邪。世常说地与人未易相遇。然山水是自在无情底物事。而人自有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2H 页
 閒忙趣舍之不同。其或遇或不遇人也。自在者何与焉。今余之于此岸也。居之近谋之久。亦且痼于心矣。北山之灵。诚不以我为俗士。杜其轮而埽其迹。使我得遂其分山一半之愿。则无分者终必有分。优游而乐馀年。尚何论人与地遇不遇于其间哉。但其交于两山。水石不得其平。似过于幽深险僻而少从容宽旷之趣。是则余亦不能无病焉。然入山者犹恐不深。其所以为病。祇足以副遁世无求自适其适之意。容何病焉。姑记上下九节旧呼新号之意如此。若其春秋花叶。朝暮烟云。鱼鸟之相羊。耕樵之与人。以至于佔毕忘老之乐。欲言而不可穷者。俟屋成可以言。月日。山中客书。
閒忙趣舍之不同。其或遇或不遇人也。自在者何与焉。今余之于此岸也。居之近谋之久。亦且痼于心矣。北山之灵。诚不以我为俗士。杜其轮而埽其迹。使我得遂其分山一半之愿。则无分者终必有分。优游而乐馀年。尚何论人与地遇不遇于其间哉。但其交于两山。水石不得其平。似过于幽深险僻而少从容宽旷之趣。是则余亦不能无病焉。然入山者犹恐不深。其所以为病。祇足以副遁世无求自适其适之意。容何病焉。姑记上下九节旧呼新号之意如此。若其春秋花叶。朝暮烟云。鱼鸟之相羊。耕樵之与人。以至于佔毕忘老之乐。欲言而不可穷者。俟屋成可以言。月日。山中客书。池洞丘墓记
洞在青松府治西五十里安德县之东。取捷踰岭才一里馀。北下迤从洞口而入。则殆数三里。安德权氏之世葬在焉。太师后直长讳明利。自安东避倭寇来卜峡庄。要之在本朝 太宗时。世代远。未详其相原隰卜宅兆之岁月也。山冈自南而下。左右廓开。中垂两麓。左麓圆隆而最长。从上第二。四方石筑。坟高仅四尺者。乃直长公葬也。前第三直长孙讳穆坟也。有石人小石床。第一讳恢坟也。第四讳忱坟也。与第一坟为兄弟。并直长玄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2L 页
 孙而忱无后。第五直长五世孙讳继昌坟也。两麓未分。山冈左一条西驰中低。渐西渐高。比两麓倍之。隆然中高而北下。以拱于左麓之左冈势中高处。安德县人称谓南山者也。东下廓展坡坦。突成山穴。有石砌连坟。直长曾孙讳干坟也。公有至行。尝居庐于左麓第三坟下。泣血三年。至今其涧壑称为殡所洞云。公娶闻韶金氏。青溪先生琎。金氏甥也。因缘姑母。来学于公。尝记行略。养志参孝。厚葬轲仁。书其下云居门下十年。目睹其实云。右麓上双坟。讳悛坟也。与左麓第一第四坟。为兄弟而无后。其前一坟。传称都令主山所。而未详其某行也。又其前第一坟。即我曾祖考小室闻韶金氏坟也。年十六。来奉我家。至七十九而终。无愧于古女士焉。最上入头处稍左一坟。即吾未笄女所埋也。山冈之西驰中低也。北垂一麓如冬瓜状。第七弟湜坟也。其渐西而高未半。忽抽一麓坐申者。即第五弟浤坟也。南山下双坟左小麓一坟。即以根前娶赵氏坟也。自此夷而渐下垂尽处。即七弟遗块大男坟也。自此经左小麓稍上。后夷而前陡有一穴。即第四弟潗孺人光山金氏合葬坟也。又左十馀步。即潗长子以桢坟也。通一洞久近轻重诸葬如右。直长配位乌川郑氏葬。文巨驿洞口也字局。从下
孙而忱无后。第五直长五世孙讳继昌坟也。两麓未分。山冈左一条西驰中低。渐西渐高。比两麓倍之。隆然中高而北下。以拱于左麓之左冈势中高处。安德县人称谓南山者也。东下廓展坡坦。突成山穴。有石砌连坟。直长曾孙讳干坟也。公有至行。尝居庐于左麓第三坟下。泣血三年。至今其涧壑称为殡所洞云。公娶闻韶金氏。青溪先生琎。金氏甥也。因缘姑母。来学于公。尝记行略。养志参孝。厚葬轲仁。书其下云居门下十年。目睹其实云。右麓上双坟。讳悛坟也。与左麓第一第四坟。为兄弟而无后。其前一坟。传称都令主山所。而未详其某行也。又其前第一坟。即我曾祖考小室闻韶金氏坟也。年十六。来奉我家。至七十九而终。无愧于古女士焉。最上入头处稍左一坟。即吾未笄女所埋也。山冈之西驰中低也。北垂一麓如冬瓜状。第七弟湜坟也。其渐西而高未半。忽抽一麓坐申者。即第五弟浤坟也。南山下双坟左小麓一坟。即以根前娶赵氏坟也。自此夷而渐下垂尽处。即七弟遗块大男坟也。自此经左小麓稍上。后夷而前陡有一穴。即第四弟潗孺人光山金氏合葬坟也。又左十馀步。即潗长子以桢坟也。通一洞久近轻重诸葬如右。直长配位乌川郑氏葬。文巨驿洞口也字局。从下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3H 页
 第二坟也。其后即鸡城君孙士晟内外坟也。其前即骊兴闵氏双坟也。鸡城君即直长公女婿。而闵氏即鸡城君女婿。经两姓许葬女婿。后入为主。闵氏世葬其上。直长三子长讳自庸真宝县监。乃曾王考本生派也。次讳自恭无后。次讳自诚。乃曾王考所后派也。县监墓未详所在。池洞白虎外分枝。东北行龙八九脊。又成一大局。其下即右池洞。今称愚智洞。然是在中冈白虎之外。想必右池洞之名。转而云愚智也。中间离脉垂下成一坐。离之原有大葬。传疑是县监墓。而无墓表未敢质定。其后枕主冈离坐。即继妣赵氏新葬也。自此以下主冈圆隆。顿而起一峰最高曰马峰也。横出庚行数十步。跌而左落未坤行。平冈百馀步尽处。上一坟即中冈讳穆妣位也。下二坟即讳自诚考妣位也。其后中间枕冈横坐向紫草山一坟。即三弟灦所葬也。下有奴属先入葬者。其后马峰下庚出跌左之右开戌面用五蛇里双峰乙向一坟。即濂亡室朴氏葬也。马峰左落未丁行。居中丁坐。以观坟也。其左坂向北小坟。即十一岁儿廌所埋也。是儿夭时。已读小大学论孟。大有步骤。乙未夭于红疹。以其始生定以为以观后。埋其冢傍也。古大葬后百馀步。有突起午行三十馀步。左角未落圆隆。行百馀步。有
第二坟也。其后即鸡城君孙士晟内外坟也。其前即骊兴闵氏双坟也。鸡城君即直长公女婿。而闵氏即鸡城君女婿。经两姓许葬女婿。后入为主。闵氏世葬其上。直长三子长讳自庸真宝县监。乃曾王考本生派也。次讳自恭无后。次讳自诚。乃曾王考所后派也。县监墓未详所在。池洞白虎外分枝。东北行龙八九脊。又成一大局。其下即右池洞。今称愚智洞。然是在中冈白虎之外。想必右池洞之名。转而云愚智也。中间离脉垂下成一坐。离之原有大葬。传疑是县监墓。而无墓表未敢质定。其后枕主冈离坐。即继妣赵氏新葬也。自此以下主冈圆隆。顿而起一峰最高曰马峰也。横出庚行数十步。跌而左落未坤行。平冈百馀步尽处。上一坟即中冈讳穆妣位也。下二坟即讳自诚考妣位也。其后中间枕冈横坐向紫草山一坟。即三弟灦所葬也。下有奴属先入葬者。其后马峰下庚出跌左之右开戌面用五蛇里双峰乙向一坟。即濂亡室朴氏葬也。马峰左落未丁行。居中丁坐。以观坟也。其左坂向北小坟。即十一岁儿廌所埋也。是儿夭时。已读小大学论孟。大有步骤。乙未夭于红疹。以其始生定以为以观后。埋其冢傍也。古大葬后百馀步。有突起午行三十馀步。左角未落圆隆。行百馀步。有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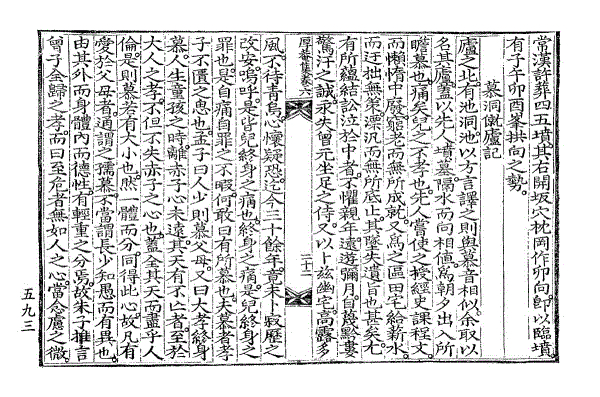 常汉许葬四五坟。其右开坂穴枕冈作卯向。即以临坟。有子午卯酉峰拱向之势。
常汉许葬四五坟。其右开坂穴枕冈作卯向。即以临坟。有子午卯酉峰拱向之势。慕洞僦庐记
庐之北。有池洞。池以方言译之则与慕音相似。余取以名其庐。盖以先人坟墓。隔水而向相值。为朝夕出入所瞻慕也。痛矣儿之不孝也。先人尝使之授经史课程文。而懒惰中废。穷老而无所成就。又为之区田宅给薪水。而迂拙无策。漂汎而无所底止。其坠失遗旨也甚矣。尤有所蕴结讼泣于中者。不惧亲年。远游弥月。自蔑黔娄惊汗之诚。永失曾元坐足之侍。又以卜玆幽宅。高露多风。不待青乌。心怀疑恐。迄今三十馀年。竟未卜寂历之改安。呜呼。是皆儿终身之痛也。终身之痛。是儿终身之罪也。是自痛自罪之不暇。何敢曰有所慕也。夫慕者孝子不匮之思也。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又曰大孝终身慕。人生童孩之时。离赤子心未远。其天有不亡者。至于大人之孝。不但不失赤子之心也。盖全其天而尽乎人伦。是则慕若有大小也。然一体而分。同得此心。故凡有爱于父母者。通谓之孺慕。不当谓长少知愚而有异也。由其外而身体内而德性。有轻重之分焉。故朱子推言曾子全归之孝。而曰至危者无如人之心。当念虑之微。
厚庵集卷之六 第 59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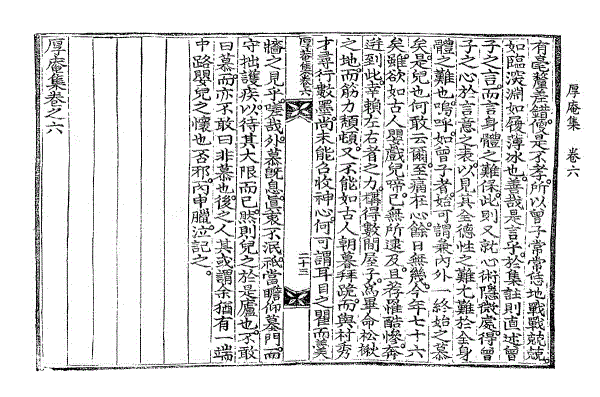 有毫釐差错。便是不孝。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善哉是言乎。于集注则直述曾子之言。而言身体之难保。此则又就心术隐微处。得曾子之心于言意之表。以见其全德性之难尤难于全身体之难也。呜呼。如曾子者。始可谓兼内外一终始之慕矣。是儿也何敢云尔。至痛在心。馀日无几。今年七十六矣。虽欲如古人婴戏儿啼。已无所逮及。且荐罹酷惨。奔迸到此。幸赖左右者之力。构得数间屋子。为毕命松楸之地。而筋力颓顿。又不能如古人朝暮拜跪。而与村秀才寻行数墨。尚未能召收神心。何可谓耳目之瞿而羹墙之见乎。嗟哉。外慕既息。真衷不泯。祇当瞻仰墓门。而守拙护疾。以待其大限而已。然则儿之于是庐也。不敢曰慕。而亦不敢曰非慕也。后之人其或谓余犹有一端中路婴儿之怀也否邪。丙申腊。泣记之。
有毫釐差错。便是不孝。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善哉是言乎。于集注则直述曾子之言。而言身体之难保。此则又就心术隐微处。得曾子之心于言意之表。以见其全德性之难尤难于全身体之难也。呜呼。如曾子者。始可谓兼内外一终始之慕矣。是儿也何敢云尔。至痛在心。馀日无几。今年七十六矣。虽欲如古人婴戏儿啼。已无所逮及。且荐罹酷惨。奔迸到此。幸赖左右者之力。构得数间屋子。为毕命松楸之地。而筋力颓顿。又不能如古人朝暮拜跪。而与村秀才寻行数墨。尚未能召收神心。何可谓耳目之瞿而羹墙之见乎。嗟哉。外慕既息。真衷不泯。祇当瞻仰墓门。而守拙护疾。以待其大限而已。然则儿之于是庐也。不敢曰慕。而亦不敢曰非慕也。后之人其或谓余犹有一端中路婴儿之怀也否邪。丙申腊。泣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