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站书库内容主要引用自 archive.org,kanripo.org, db.itkc.or.kr 和 zh.wikisource.org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x 页
晚慕遗稿卷之六
杂著
杂著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0H 页
 看书漫录
看书漫录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惟恐其不长。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或恐其渐长。此圣人扶阳抑阴之意。
屯乘马。盖取互卦。六二至六四为坤。坤为牝马。
传义于他卦则卦辞爻辞。各以其义释之。而如蒙之卦辞释九二。需之卦辞释九五之类。亦有之。
师大象容民畜众。天下之水。皆归地中。是畜众也。地能含容无泛溢之患。是容民也。
比之初六。阳实故为盈。阴虚故为缶。而终吉之义。程传引而不发。盖比初之应四也而阴不从阴。故四乃背其正应而从于九五。是初有应而无应也。然初六才柔位刚。为有孚盈缶之象。故今虽无应。而若积其诚信。则终必有来比之者也。
小畜复自道者。犹言复乃自然之道也。○九二虽刚中而位柔。其上进之健。犹不如初九之重刚。故必得牵连之力然后。方可以上进而有吉。
履初九既安其素则宜无往进之义。而今反曰往者何也。盖才位俱刚。有健行之意故言往。往是进德修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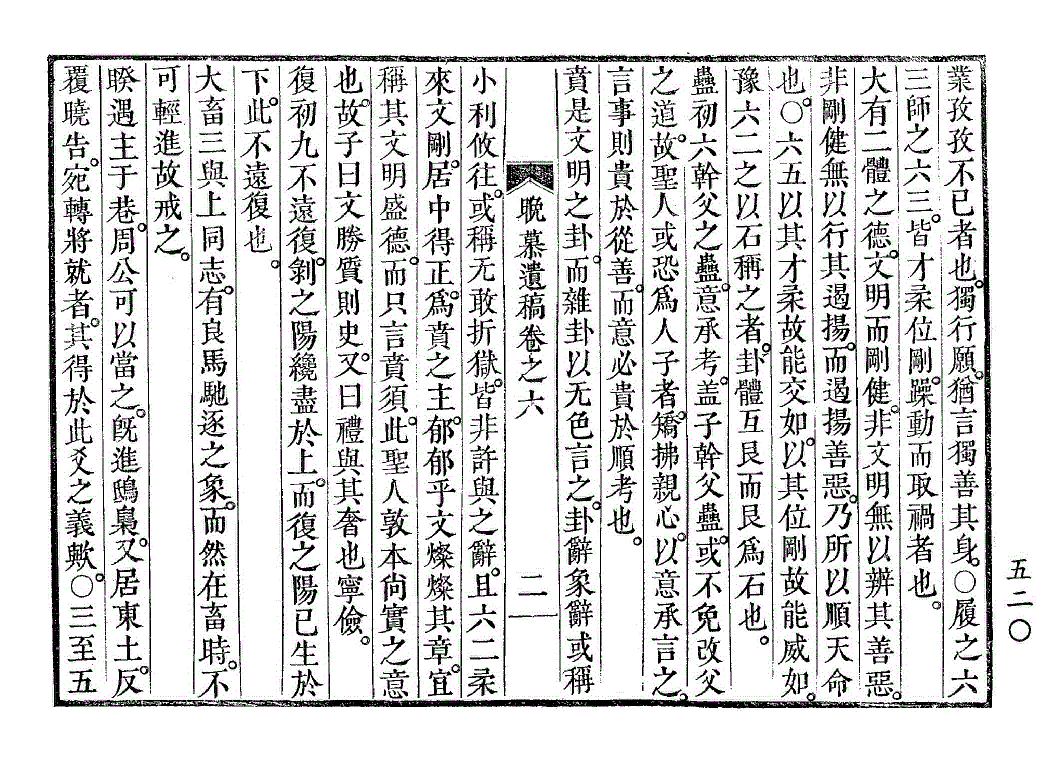 业孜孜不已者也。独行愿。犹言独善其身。○履之六三师之六三。皆才柔位刚。躁动而取祸者也。
业孜孜不已者也。独行愿。犹言独善其身。○履之六三师之六三。皆才柔位刚。躁动而取祸者也。大有二体之德。文明而刚健。非文明无以辨其善恶。非刚健无以行其遏扬。而遏扬善恶。乃所以顺天命也。○六五以其才柔故能交如。以其位刚故能威如。
豫六二之以石称之者。卦体互艮而艮为石也。
蛊初六干父之蛊。意承考。盖子干父蛊。或不免改父之道。故圣人或恐为人子者。矫拂亲心。以意承言之。言事则贵于从善。而意必贵于顺考也。
贲是文明之卦。而杂卦以无色言之。卦辞象辞或称小利攸往。或称无敢折狱。皆非许与之辞。且六二柔来文刚。居中得正。为贲之主。郁郁乎文灿灿其章。宜称其文明盛德。而只言贲须。此圣人敦本尚实之意也。故子曰文胜质则史。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
复初九不远复。剥之阳才尽于上。而复之阳已生于下。此不远复也。
大畜三与上同志。有良马驰逐之象。而然在畜时。不可轻进故戒之。
睽遇主于巷。周公可以当之。既进鸱枭。又居东土。反覆晓告。宛转将就者。其得于此爻之义欤。○三至五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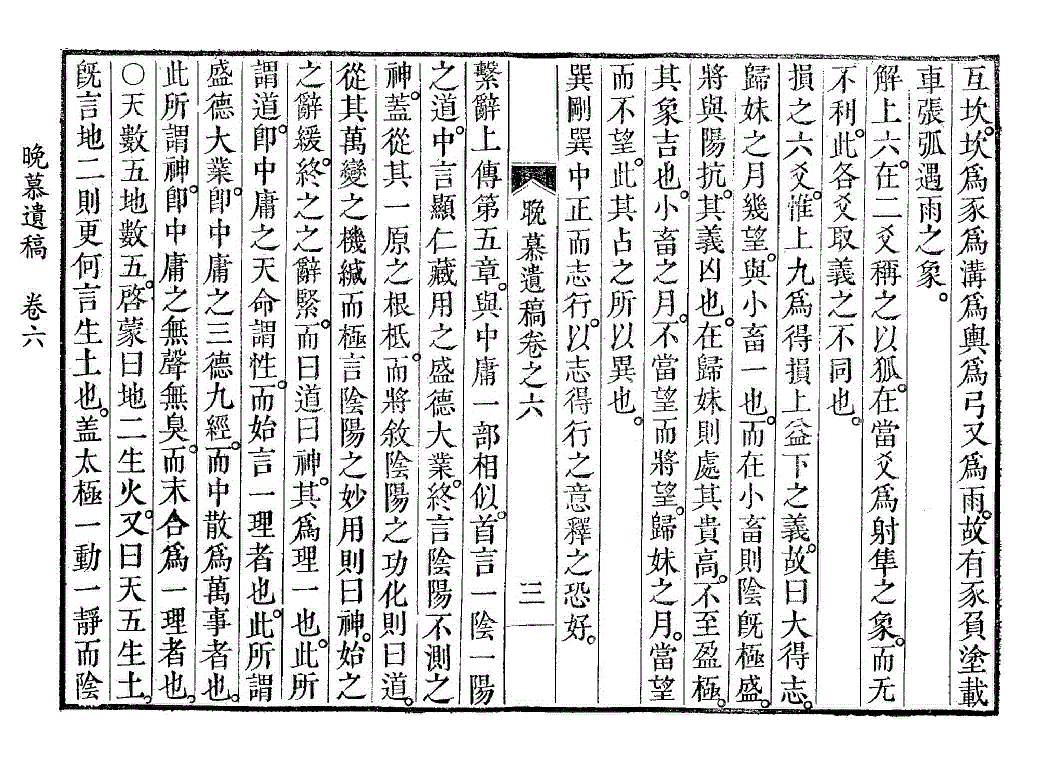 互坎。坎为豕为沟为舆为弓又为雨。故有豕负涂载车张弧遇雨之象。
互坎。坎为豕为沟为舆为弓又为雨。故有豕负涂载车张弧遇雨之象。解上六。在二爻称之以狐。在当爻为射隼之象。而无不利。此各爻取义之不同也。
损之六爻。惟上九为得损上益下之义。故曰大得志。
归妹之月几望。与小畜一也。而在小畜则阴既极盛。将与阳抗。其义凶也。在归妹则处其贵高。不至盈极。其象吉也。小畜之月。不当望而将望。归妹之月。当望而不望。此其占之所以异也。
巽刚巽中正而志行。以志得行之意释之恐好。
系辞上传第五章。与中庸一部相似。首言一阴一阳之道。中言显仁藏用之盛德大业。终言阴阳不测之神。盖从其一原之根柢。而将叙阴阳之功化则曰道。从其万变之机缄而极言阴阳之妙用则曰神。始之之辞缓。终之之辞紧。而曰道曰神。其为理一也。此所谓道。即中庸之天命谓性。而始言一理者也。此所谓盛德大业。即中庸之三德九经。而中散为万事者也。此所谓神。即中庸之无声无臭。而末合为一理者也。○天数五地数五。启蒙曰地二生火。又曰天五生土。既言地二则更何言生土也。盖太极一动一静而阴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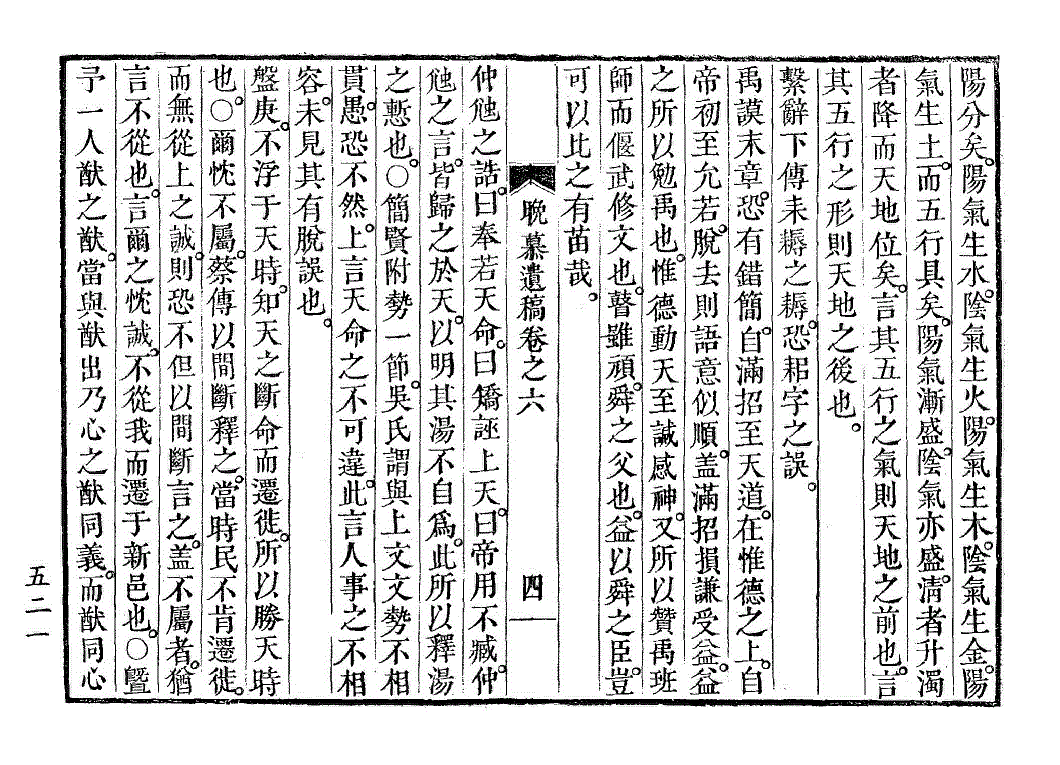 阳分矣。阳气生水。阴气生火。阳气生木。阴气生金。阳气生土。而五行具矣。阳气渐盛。阴气亦盛。清者升浊者降而天地位矣。言其五行之气则天地之前也。言其五行之形则天地之后也。
阳分矣。阳气生水。阴气生火。阳气生木。阴气生金。阳气生土。而五行具矣。阳气渐盛。阴气亦盛。清者升浊者降而天地位矣。言其五行之气则天地之前也。言其五行之形则天地之后也。系辞下传耒耨之耨。恐耜字之误。
禹谟末章。恐有错简。自满招至天道。在惟德之上。自帝初至允若。脱去则语意似顺。盖满招损谦受益。益之所以勉禹也。惟德动天至諴感神。又所以赞禹班师而偃武修文也。瞽虽顽。舜之父也。益以舜之臣。岂可以比之有苗哉。
仲虺之诰。曰奉若天命。曰矫诬上天。曰帝用不臧。仲虺之言。皆归之于天。以明其汤不自为。此所以释汤之惭也。○简贤附势一节。吴氏谓与上文文势不相贯。愚恐不然。上言天命之不可违。此言人事之不相容。未见其有脱误也。
盘庚。不浮于天时。知天之断命而迁徙。所以胜天时也。○尔忱不属。蔡传以间断释之。当时民不肯迁徙。而无从上之诚。则恐不但以间断言之。盖不属者。犹言不从也。言尔之忱诚。不从我而迁于新邑也。○暨予一人猷之猷。当与猷出乃心之猷同义。而猷同心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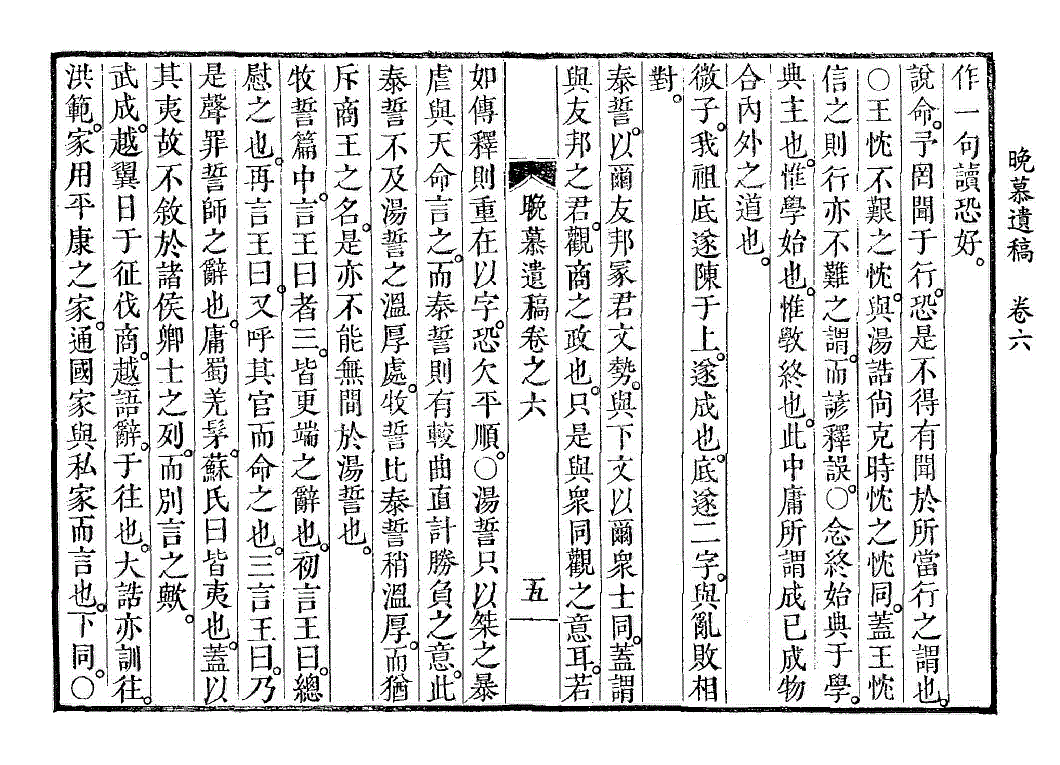 作一句读恐好。
作一句读恐好。说命。予罔闻于行。恐是不得有闻于所当行之谓也。○王忱不艰之忱。与汤诰尚克时忱之忱同。盖王忱信之则行亦不难之谓。而谚释误。○念终始典于学。典主也。惟学始也。惟敩终也。此中庸所谓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也。
微子。我祖底遂陈于上。遂成也。底遂二字。与乱败相对。
泰誓。以尔友邦冢君文势。与下文以尔众士同。盖谓与友邦之君。观商之政也。只是与众同观之意耳。若如传释则重在以字。恐欠平顺。○汤誓只以桀之暴虐与天命言之。而泰誓则有较曲直计胜负之意。此泰誓不及汤誓之温厚处。牧誓比泰誓稍温厚。而犹斥商王之名。是亦不能无间于汤誓也。
牧誓篇中。言王曰者三。皆更端之辞也。初言王曰。总慰之也。再言王曰。又呼其官而命之也。三言王曰。乃是声罪誓师之辞也。庸蜀羌髳。苏氏曰皆夷也。盖以其夷故不叙于诸侯卿士之列。而别言之欤。
武成。越翼日于征伐商。越语辞。于往也。大诰亦训往。
洪范。家用平康之家。通国家与私家而言也。下同。○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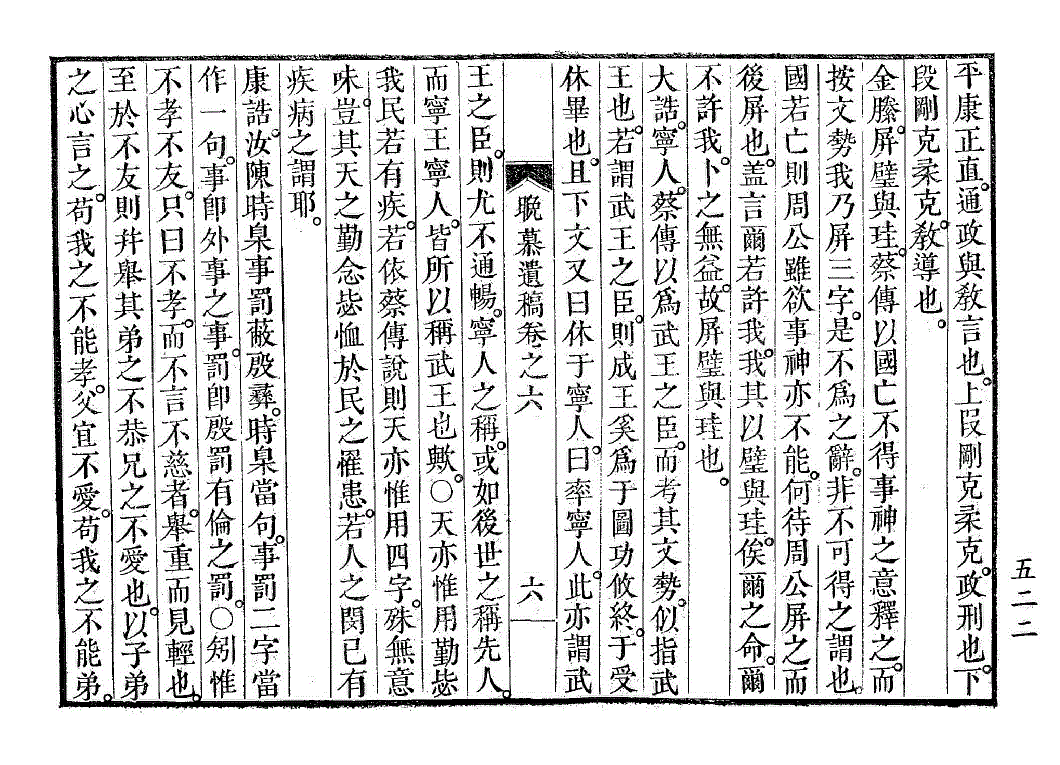 平康正直。通政与教言也。上段刚克柔克。政刑也。下段刚克柔克。教导也。
平康正直。通政与教言也。上段刚克柔克。政刑也。下段刚克柔克。教导也。金縢。屏璧与圭。蔡传以国亡不得事神之意释之。而按文势我乃屏三字。是不为之辞。非不可得之谓也。国若亡则周公虽欲事神亦不能。何待周公屏之而后屏也。盖言尔若许我。我其以璧与圭。俟尔之命。尔不许我。卜之无益。故屏璧与圭也。
大诰。宁人。蔡传以为武王之臣。而考其文势。似指武王也。若谓武王之臣。则成王奚为于图功攸终。于受休毕也。且下文又曰休于宁人。曰率宁人。此亦谓武王之臣。则尤不通畅。宁人之称。或如后世之称先人。而宁王宁人。皆所以称武王也欤。○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若依蔡传说则天亦惟用四字。殊无意味。岂其天之勤念毖恤于民之罹患。若人之闵己有疾病之谓耶。
康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时臬当句。事罚二字当作一句。事即外事之事。罚即殷罚有伦之罚。○矧惟不孝不友。只曰不孝。而不言不慈者。举重而见轻也。至于不友则并举其弟之不恭兄之不爱也。以子弟之心言之。苟我之不能孝。父宜不爱。苟我之不能弟。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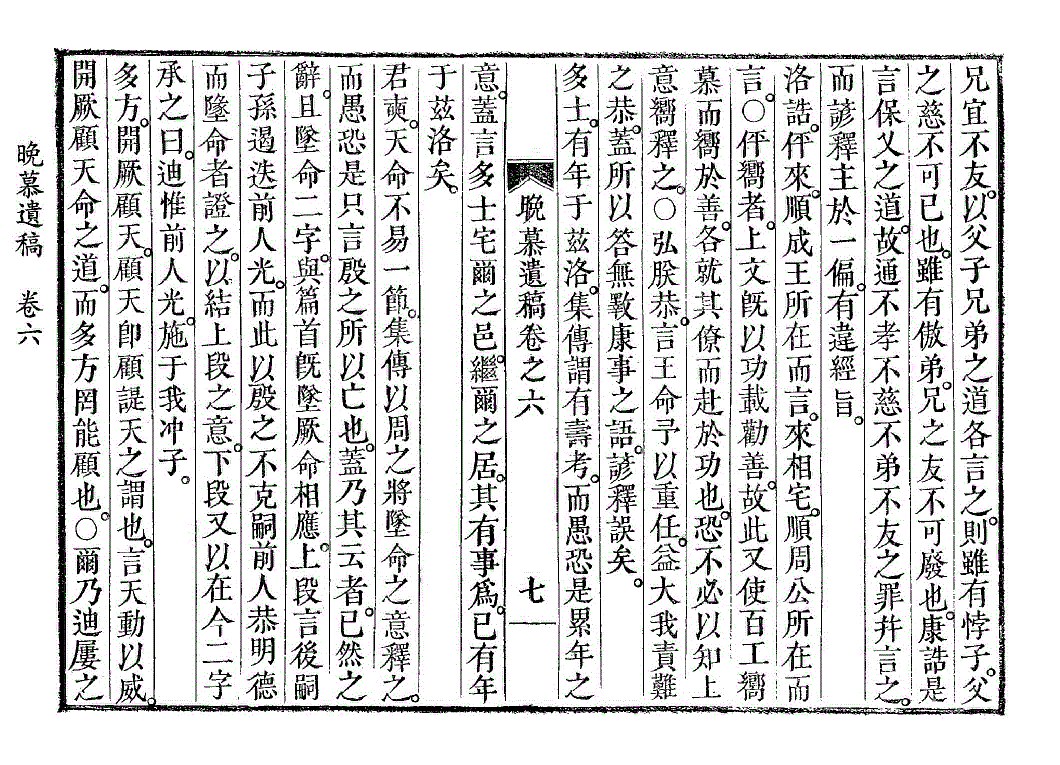 兄宜不友。以父子兄弟之道各言之。则虽有悖子。父之慈不可已也。虽有傲弟。兄之友不可废也。康诰是言保乂之道。故通不孝不慈不弟不友之罪并言之。而谚释主于一偏。有违经旨。
兄宜不友。以父子兄弟之道各言之。则虽有悖子。父之慈不可已也。虽有傲弟。兄之友不可废也。康诰是言保乂之道。故通不孝不慈不弟不友之罪并言之。而谚释主于一偏。有违经旨。洛诰。伻来。顺成王所在而言。来相宅。顺周公所在而言。○伻向者。上文既以功载劝善。故此又使百工向慕而向于善。各就其僚而赴于功也。恐不必以知上意向释之。○弘朕恭。言王命予以重任。益大我责难之恭。盖所以答无斁康事之语。谚释误矣。
多士。有年于玆洛。集传谓有寿考。而愚恐是累年之意。盖言多士宅尔之邑。继尔之居。其有事为。已有年于玆洛矣。
君奭。天命不易一节。集传以周之将坠命之意释之。而愚恐是只言殷之所以亡也。盖乃其云者。已然之辞。且坠命二字。与篇首既坠厥命相应。上段言后嗣子孙遏迭前人光。而此以殷之不克嗣前人恭明德而坠命者證之。以结上段之意。下段又以在今二字承之曰。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多方。开厥顾天。顾天即顾諟天之谓也。言天动以威。开厥顾天命之道。而多方罔能顾也。○尔乃迪屡之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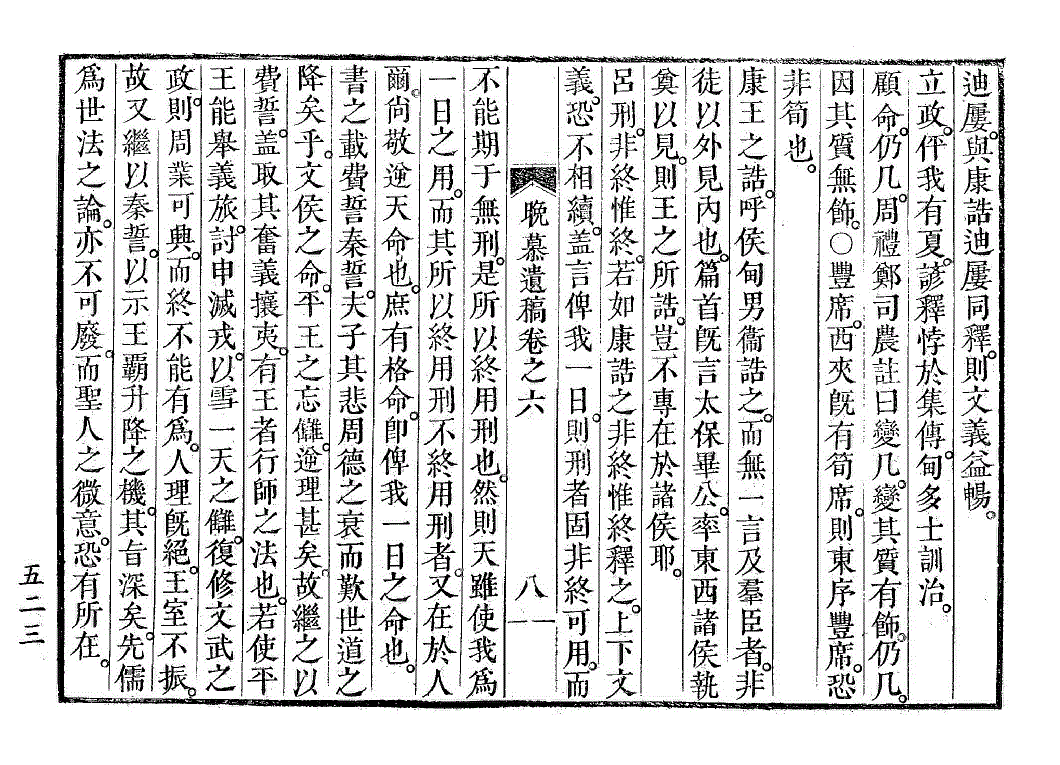 迪屡。与康诰迪屡同释。则文义益畅。
迪屡。与康诰迪屡同释。则文义益畅。立政。伻我有夏。谚释悖于集传。甸多士训治。
顾命。仍几。周礼郑司农注曰变几。变其质有饰。仍几。因其质无饰。○丰席。西夹既有笋席。则东序丰席。恐非笋也。
康王之诰。呼侯甸男卫诰之。而无一言及群臣者。非徒以外见内也。篇首既言太保毕公。率东西诸侯执奠以见。则王之所诰。岂不专在于诸侯耶。
吕刑。非终惟终。若如康诰之非终惟终释之。上下文义。恐不相续。盖言俾我一日。则刑者固非终可用。而不能期于无刑。是所以终用刑也。然则天虽使我为一日之用。而其所以终用刑不终用刑者。又在于人尔。尚敬逆天命也。庶有格命。即俾我一日之命也。
书之载费誓秦誓。夫子其悲周德之衰。而叹世道之降矣乎。文侯之命。平王之忘雠。逆理甚矣。故继之以费誓。盖取其奋义攘夷。有王者行师之法也。若使平王能举义旅。讨申灭戎。以雪一天之雠。复修文武之政。则周业可兴。而终不能有为。人理既绝。王室不振。故又继以秦誓。以示王霸升降之机。其旨深矣。先儒为世法之论。亦不可废。而圣人之微意。恐有所在。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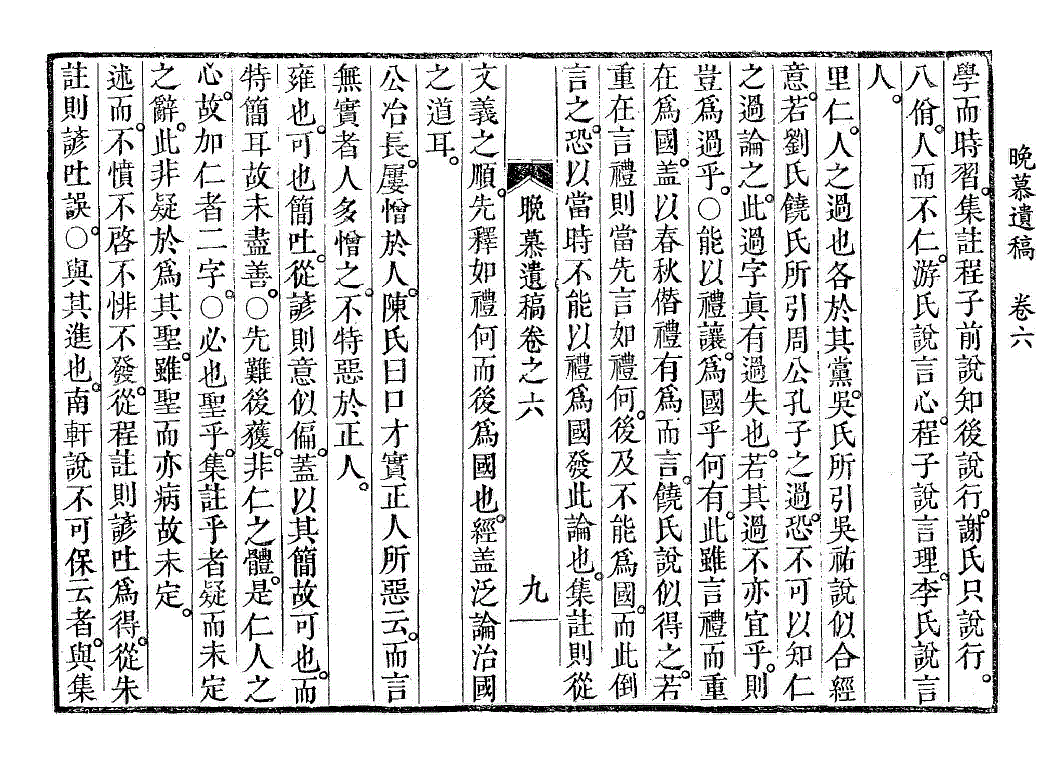 学而时习。集注程子前说知后说行。谢氏只说行。
学而时习。集注程子前说知后说行。谢氏只说行。八佾。人而不仁。游氏说言心。程子说言理。李氏说言人。
里仁。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吴氏所引吴祐说似合经意。若刘氏饶氏所引周公孔子之过。恐不可以知仁之过论之。此过字真有过失也。若其过不亦宜乎。则岂为过乎。○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此虽言礼而重在为国。盖以春秋僭礼有为而言。饶氏说似得之。若重在言礼则当先言如礼何。后及不能为国。而此倒言之。恐以当时不能以礼为国发此论也。集注则从文义之顺。先释如礼何而后为国也。经盖泛论治国之道耳。
公冶长。屡憎于人。陈氏曰口才实正人所恶云。而言无实者人多憎之。不特恶于正人。
雍也。可也简吐。从谚则意似偏。盖以其简故可也。而特简耳故未尽善。○先难后获。非仁之体。是仁人之心。故加仁者二字。○必也圣乎。集注乎者疑而未定之辞。此非疑于为其圣。虽圣而亦病故未定。
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从程注则谚吐为得。从朱注则谚吐误。○与其进也。南轩说不可保云者。与集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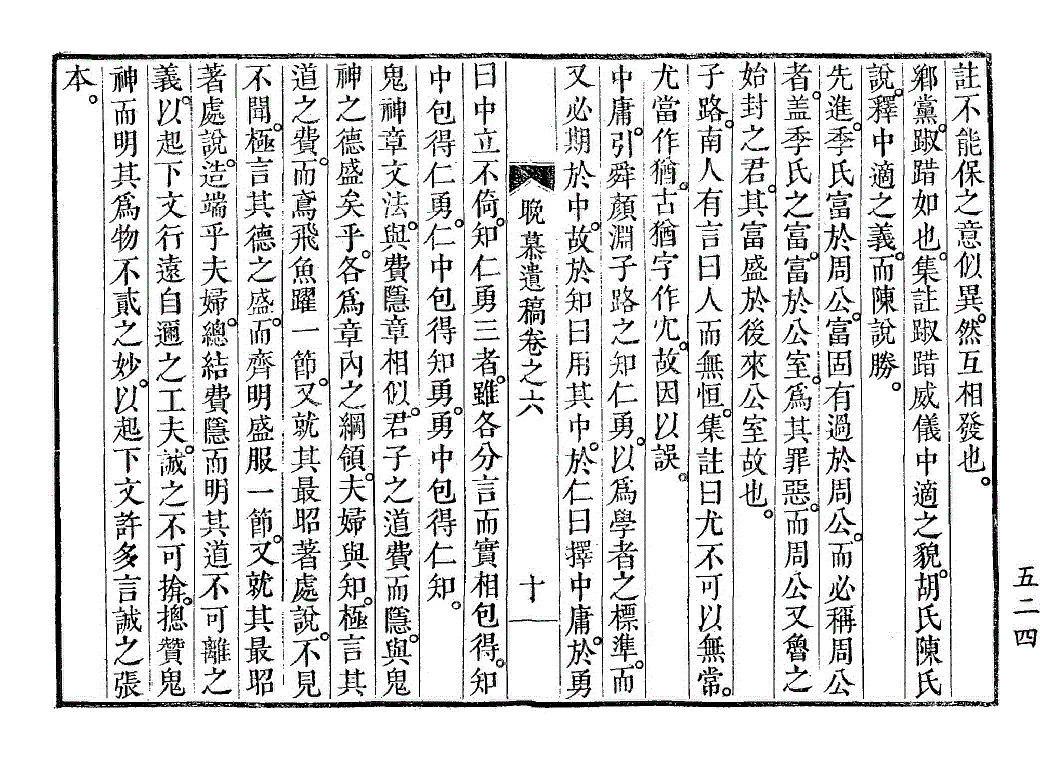 注不能保之意似异。然互相发也。
注不能保之意似异。然互相发也。乡党。踧踖如也。集注踧踖威仪中适之貌。胡氏陈氏说。释中适之义。而陈说胜。
先进。季氏富于周公。富固有过于周公。而必称周公者。盖季氏之富。富于公室。为其罪恶。而周公又鲁之始封之君。其富盛于后来公室故也。
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集注曰尤不可以无常。尤当作犹。古犹字作冘。故因以误。
中庸。引舜颜渊子路之知仁勇。以为学者之标准。而又必期于中。故于知曰用其中。于仁曰择中庸。于勇曰中立不倚。知仁勇三者。虽各分言而实相包得。知中包得仁勇。仁中包得知勇。勇中包得仁知。
鬼神章文法。与费隐章相似。君子之道费而隐。与鬼神之德盛矣乎。各为章内之纲领。夫妇与知。极言其道之费。而鸢飞鱼跃一节。又就其最昭著处说。不见不闻。极言其德之盛。而齐明盛服一节。又就其最昭著处说。造端乎夫妇。总结费隐而明其道不可离之义。以起下文行远自迩之工夫。诚之不可掩。总赞鬼神而明其为物不贰之妙。以起下文许多言诚之张本。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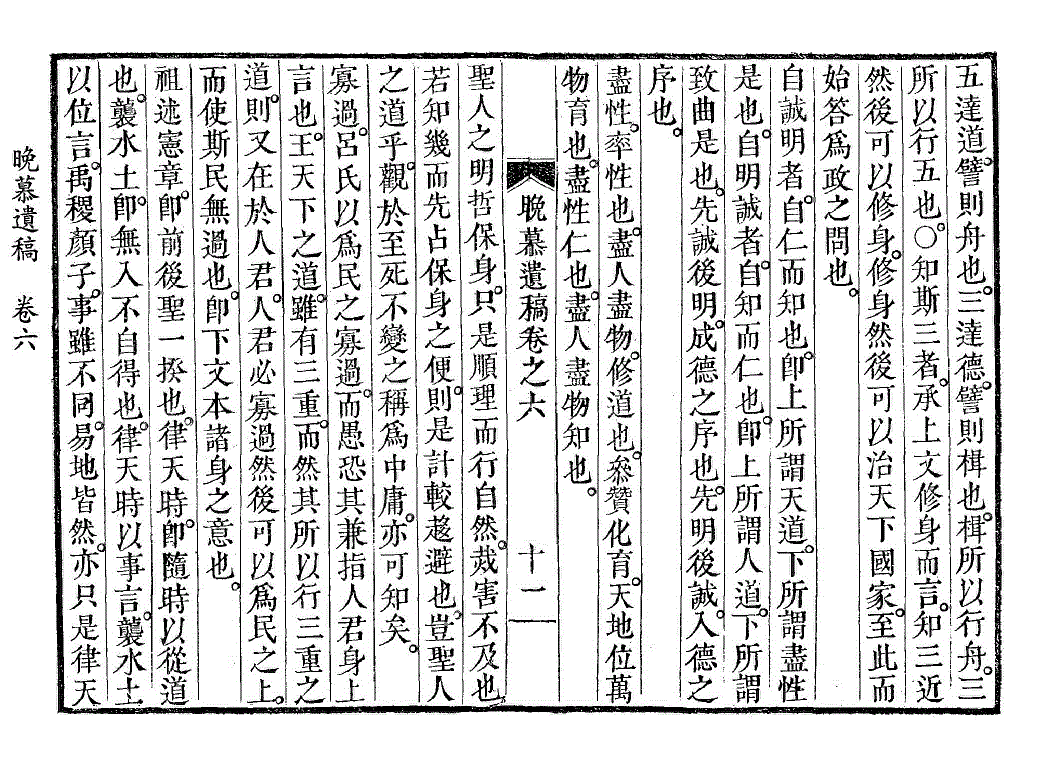 五达道。譬则舟也。三达德。譬则楫也。楫所以行舟。三所以行五也。○知斯三者。承上文修身而言。知三近然后可以修身。修身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至此而始答为政之问也。
五达道。譬则舟也。三达德。譬则楫也。楫所以行舟。三所以行五也。○知斯三者。承上文修身而言。知三近然后可以修身。修身然后可以治天下国家。至此而始答为政之问也。自诚明者。自仁而知也。即上所谓天道。下所谓尽性是也。自明诚者。自知而仁也。即上所谓人道。下所谓致曲是也。先诚后明。成德之序也。先明后诚。入德之序也。
尽性。率性也。尽人尽物。修道也。参赞化育。天地位万物育也。尽性仁也。尽人尽物知也。
圣人之明哲保身。只是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也。若知几而先占保身之便。则是计较趍避也。岂圣人之道乎。观于至死不变之称为中庸。亦可知矣。
寡过。吕氏以为民之寡过。而愚恐其兼指人君身上言也。王天下之道。虽有三重。而然其所以行三重之道。则又在于人君。人君必寡过然后可以为民之上。而使斯民无过也。即下文本诸身之意也。
祖述宪章。即前后圣一揆也。律天时。即随时以从道也。袭水土。即无入不自得也。律天时以事言。袭水土以位言。禹稷颜子。事虽不同。易地皆然。亦只是律天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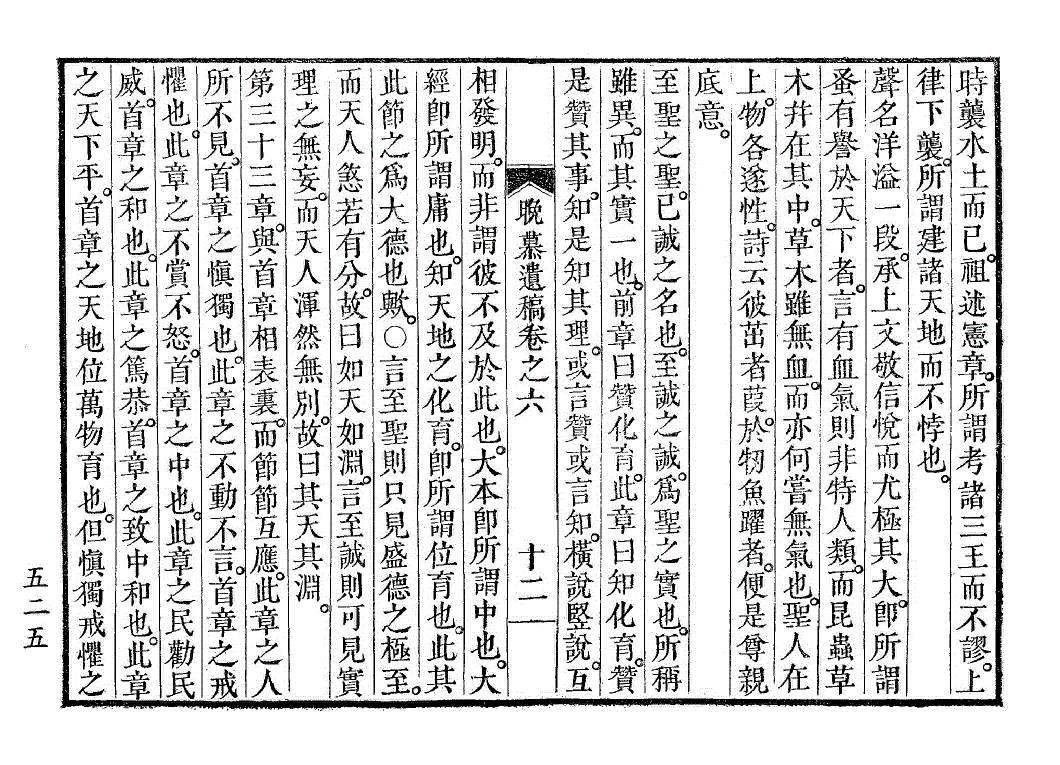 时袭水土而已。祖述宪章。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上律下袭。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也。
时袭水土而已。祖述宪章。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上律下袭。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也。声名洋溢一段。承上文敬信悦而尤极其大。即所谓蚤有誉于天下者。言有血气则非特人类。而昆虫草木并在其中。草木虽无血。而亦何尝无气也。圣人在上。物各遂性。诗云彼茁者葭。于牣鱼跃者。便是尊亲底意。
至圣之圣。已诚之名也。至诚之诚。为圣之实也。所称虽异。而其实一也。前章曰赞化育。此章曰知化育。赞是赞其事。知是知其理。或言赞或言知。横说竖说。互相发明。而非谓彼不及于此也。大本即所谓中也。大经即所谓庸也。知天地之化育。即所谓位育也。此其此节之为大德也欤。○言至圣则只见盛德之极至。而天人煞若有分。故曰如天如渊。言至诚则可见实理之无妄。而天人浑然无别。故曰其天其渊。
第三十三章。与首章相表里。而节节互应。此章之人所不见。首章之慎独也。此章之不动不言。首章之戒惧也。此章之不赏不怒。首章之中也。此章之民劝民威。首章之和也。此章之笃恭。首章之致中和也。此章之天下平。首章之天地位万物育也。但慎独戒惧之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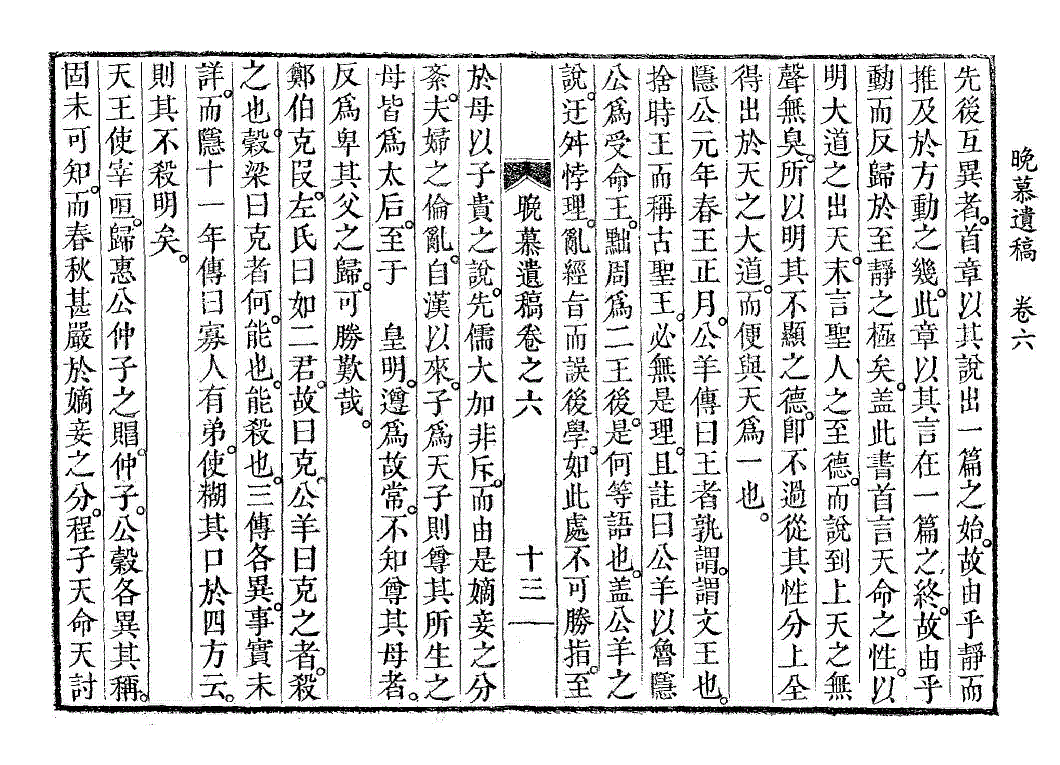 先后互异者。首章以其说出一篇之始。故由乎静而推及于方动之几。此章以其言在一篇之终。故由乎动而反归于至静之极矣。盖此书首言天命之性。以明大道之出天。末言圣人之至德。而说到上天之无声无臭。所以明其不显之德。即不过从其性分上全得出于天之大道。而便与天为一也。
先后互异者。首章以其说出一篇之始。故由乎静而推及于方动之几。此章以其言在一篇之终。故由乎动而反归于至静之极矣。盖此书首言天命之性。以明大道之出天。末言圣人之至德。而说到上天之无声无臭。所以明其不显之德。即不过从其性分上全得出于天之大道。而便与天为一也。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舍时王而称古圣王。必无是理。且注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是何等语也。盖公羊之说。迂舛悖理。乱经旨而误后学。如此处不可胜指。至于母以子贵之说。先儒大加非斥。而由是嫡妾之分紊。夫妇之伦乱。自汉以来。子为天子则尊其所生之母皆为太后。至于 皇明。遵为故常。不知尊其母者。反为卑其父之归。可胜叹哉。
郑伯克段。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公羊曰克之者。杀之也。谷梁曰克者何。能也。能杀也。三传各异。事实未详。而隐十一年传曰寡人有弟。使糊其口于四方云。则其不杀明矣。
天王使宰咺。归惠公仲子之赗。仲子。公谷各异其称。固未可知。而春秋甚严于嫡妾之分。程子天命天讨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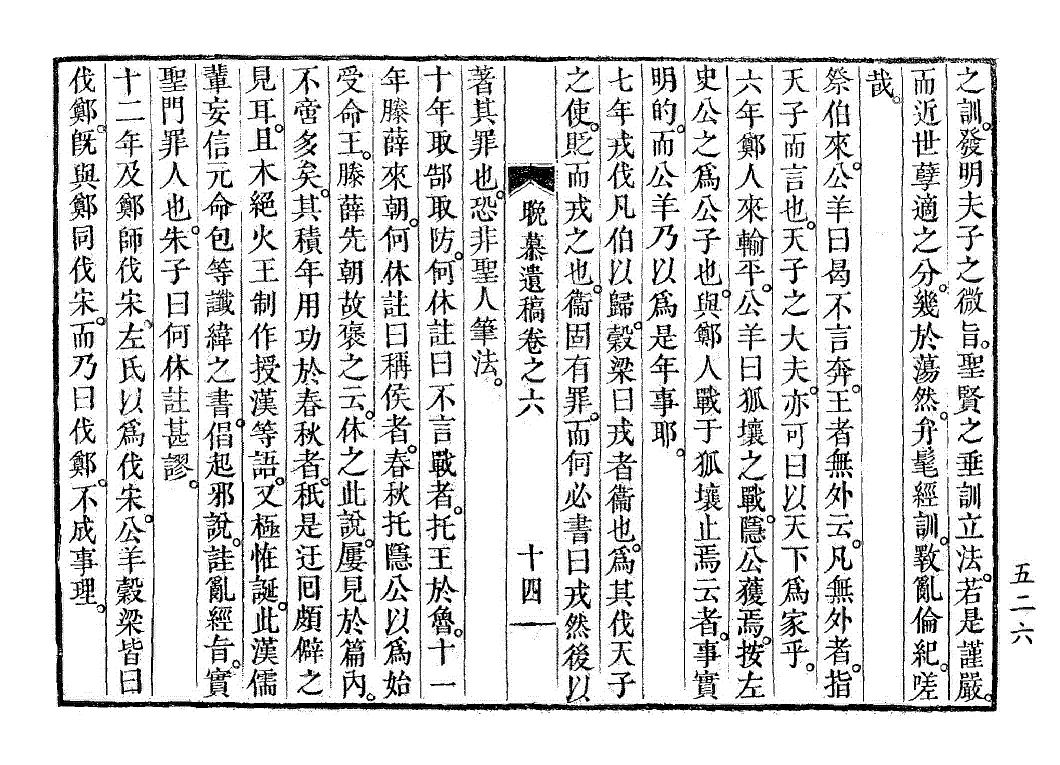 之训。发明夫子之微旨。圣贤之垂训立法。若是谨严。而近世孽适之分。几于荡然。弁髦经训。斁乱伦纪。嗟哉。
之训。发明夫子之微旨。圣贤之垂训立法。若是谨严。而近世孽适之分。几于荡然。弁髦经训。斁乱伦纪。嗟哉。祭伯来。公羊曰曷不言奔。王者无外云。凡无外者。指天子而言也。天子之大夫。亦可曰以天下为家乎。
六年郑人来输平。公羊曰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按左史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云者。事实明的。而公羊乃以为是年事耶。
七年戎伐凡伯以归。谷梁曰戎者卫也。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卫固有罪。而何必书曰戎然后以著其罪也。恐非圣人笔法。
十年取郜取防。何休注曰不言战者。托王于鲁。十一年滕薛来朝。何休注曰称侯者。春秋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故褒之云。休之此说。屡见于篇内。不啻多矣。其积年用功于春秋者。秖是迂回颇僻之见耳。且木绝火王制作授汉等语。又极怪诞。此汉儒辈妄信元命包等谶纬之书。倡起邪说。诖乱经旨。实圣门罪人也。朱子曰何休注甚谬。
十二年及郑师伐宋。左氏以为伐宋。公羊谷梁皆曰伐郑。既与郑同伐宋。而乃曰伐郑。不成事理。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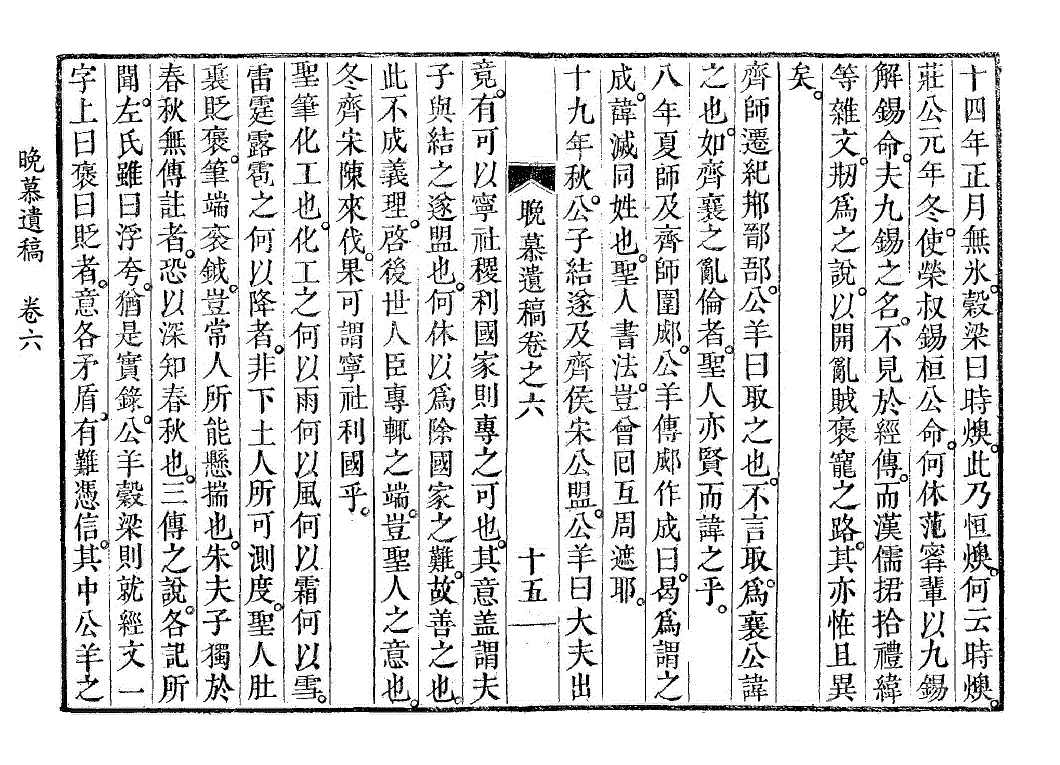 十四年正月无冰。谷梁曰时燠。此乃恒燠。何云时燠。
十四年正月无冰。谷梁曰时燠。此乃恒燠。何云时燠。庄公元年冬。使荣叔锡桓公命。何休范宁辈以九锡解锡命。夫九锡之名。不见于经传。而汉儒捃拾礼纬等杂文。刱为之说。以开乱贼褒宠之路。其亦怪且异矣。
齐师迁纪郱鄑郚。公羊曰取之也。不言取。为襄公讳之也。如齐襄之乱伦者。圣人亦贤而讳之乎。
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公羊传郕作成曰。曷为谓之成。讳灭同姓也。圣人书法。岂曾回互周遮耶。
十九年秋。公子结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竟。有可以宁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其意盖谓夫子与结之遂盟也。何休以为除国家之难。故善之也。此不成义理。启后世人臣专辄之端。岂圣人之意也。冬齐宋陈来伐。果可谓宁社利国乎。
圣笔化工也。化工之何以雨何以风何以霜何以雪。雷霆露雹之何以降者。非下土人所可测度。圣人肚里贬褒。笔端衮钺。岂常人所能悬揣也。朱夫子独于春秋无传注者。恐以深知春秋也。三传之说。各记所闻。左氏虽曰浮夸。犹是实录。公羊谷梁。则就经文一字上曰褒曰贬者。意各矛盾。有难凭信。其中公羊之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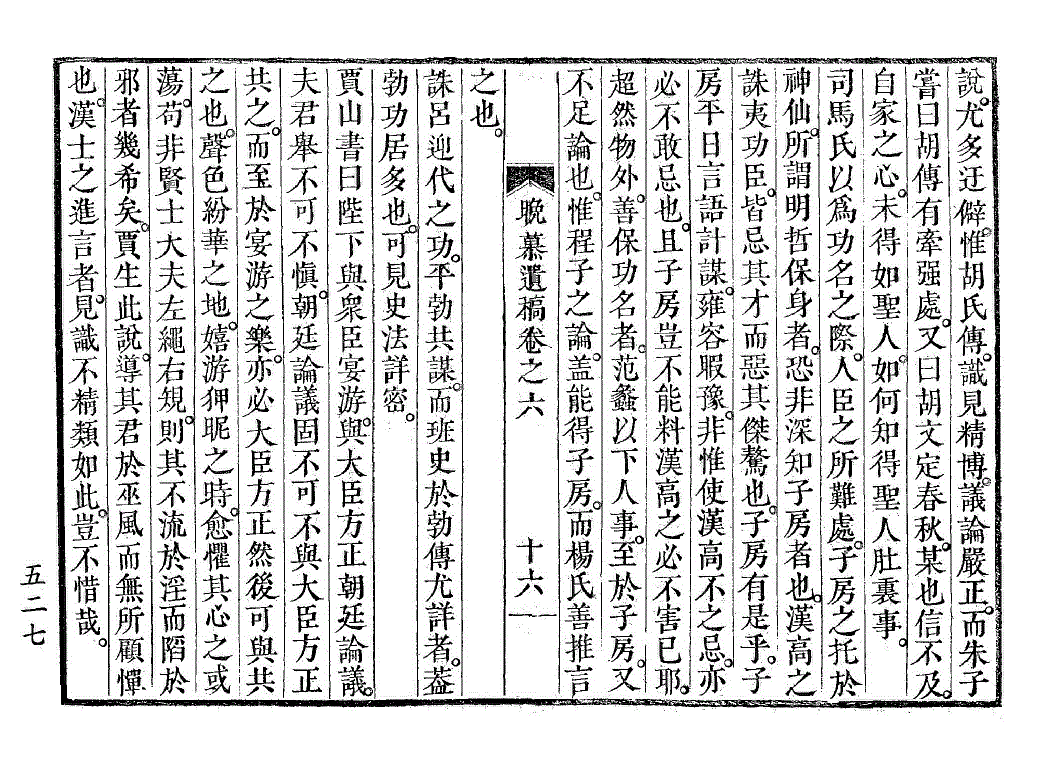 说。尤多迂僻。惟胡氏传。识见精博。议论严正。而朱子尝曰胡传有牵强处。又曰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自家之心。未得如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
说。尤多迂僻。惟胡氏传。识见精博。议论严正。而朱子尝曰胡传有牵强处。又曰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自家之心。未得如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司马氏以为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子房之托于神仙。所谓明哲保身者。恐非深知子房者也。汉高之诛夷功臣。皆忌其才而恶其杰骜也。子房有是乎。子房平日言语计谋。雍容暇豫。非惟使汉高不之忌。亦必不敢忌也。且子房岂不能料汉高之必不害己耶。超然物外。善保功名者。范蠡以下人事。至于子房。又不足论也。惟程子之论。盖能得子房。而杨氏善推言之也。
诛吕迎代之功。平勃共谋。而班史于勃传尤详者。盖勃功居多也。可见史法详密。
贾山书曰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君举不可不慎。朝廷论议。固不可不与大臣方正共之。而至于宴游之乐。亦必大臣方正然后可与共之也。声色纷华之地。嬉游狎昵之时。愈惧其心之或荡。苟非贤士大夫左绳右规。则其不流于淫。而陷于邪者几希矣。贾生此说。导其君于巫风而无所顾惮也。汉士之进言者。见识不精类如此。岂不惜哉。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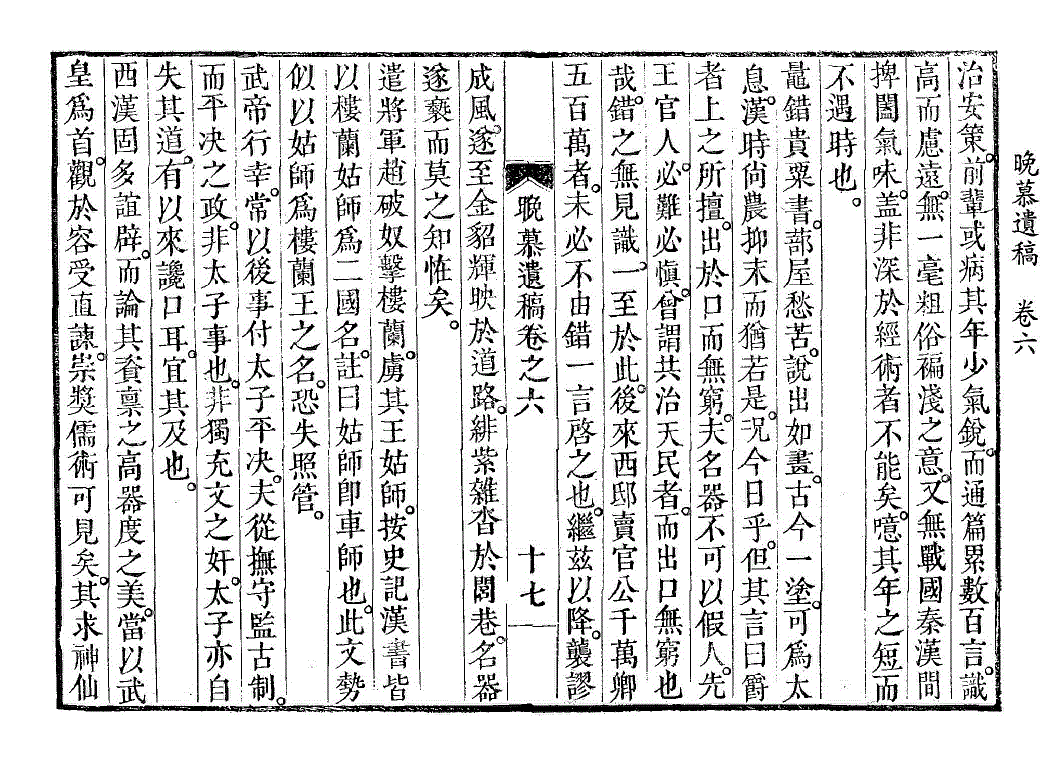 治安策。前辈或病其年少气锐。而通篇累数百言。识高而虑远。无一毫粗俗褊浅之意。又无战国秦汉间捭阖气味。盖非深于经术者不能矣。噫其年之短而不遇时也。
治安策。前辈或病其年少气锐。而通篇累数百言。识高而虑远。无一毫粗俗褊浅之意。又无战国秦汉间捭阖气味。盖非深于经术者不能矣。噫其年之短而不遇时也。晁错贵粟书。蔀屋愁苦。说出如画。古今一涂。可为太息。汉时尚农抑末而犹若是。况今日乎。但其言曰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夫名器不可以假人。先王官人。必难必慎。曾谓共治天民者。而出口无穷也哉。错之无见识。一至于此。后来西邸卖官公千万卿五百万者。未必不由错一言启之也。继玆以降。袭谬成风。遂至金貂辉映于道路。绯紫杂沓于闾巷。名器遂亵而莫之知怪矣。
遣将军赵破奴击楼兰。虏其王姑师。按史记汉书。皆以楼兰姑师为二国名。注曰姑师即车师也。此文势似以姑师为楼兰王之名。恐失照管。
武帝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平决。夫从抚守监古制。而平决之政。非太子事也。非独充文之奸。太子亦自失其道。有以来谗口耳。宜其及也。
西汉固多谊辟。而论其资禀之高器度之美。当以武皇为首。观于容受直谏。崇奖儒术可见矣。其求神仙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8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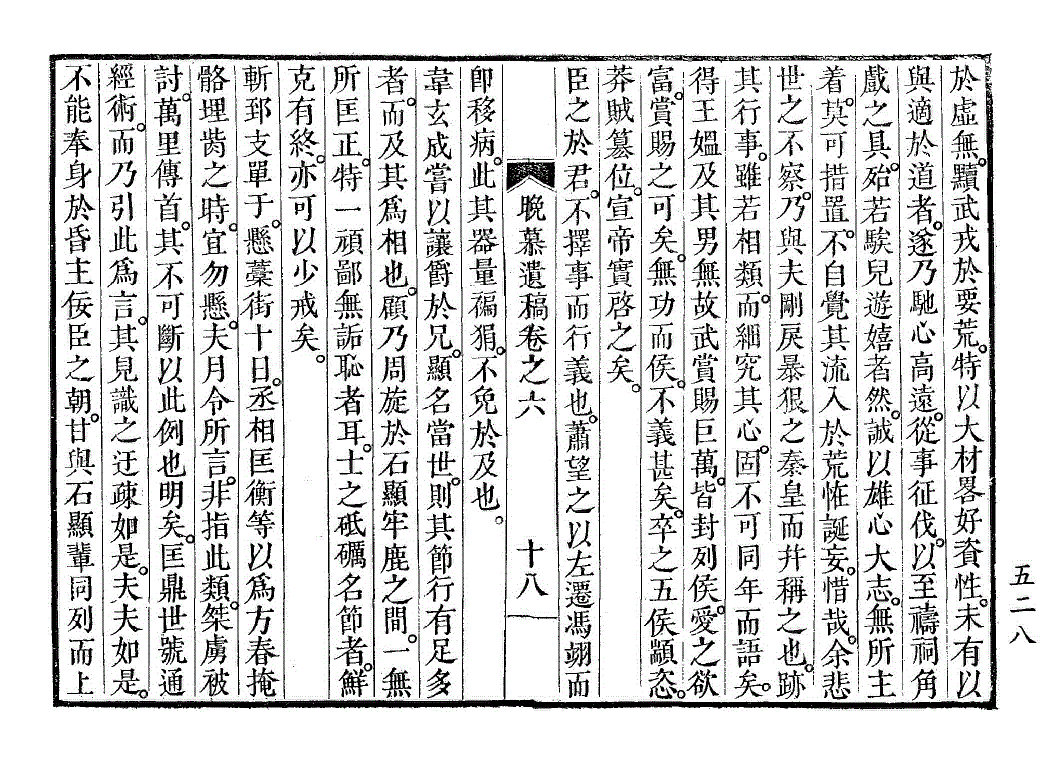 于虚无。黩武戎于要荒。特以大材略好资性。未有以与适于道者。遂乃驰心高远。从事征伐。以至祷祠角戏之具。殆若騃儿游嬉者然。诚以雄心大志。无所主着。莫可措置。不自觉其流入于荒怪诞妄。惜哉。余悲世之不察。乃与夫刚戾暴狠之秦皇而并称之也。迹其行事。虽若相类。而细究其心。固不可同年而语矣。得王媪及其男无故武赏赐巨万。皆封列侯。爱之欲富。赏赐之可矣。无功而侯。不义甚矣。卒之五侯颛恣。莽贼篡位。宣帝实启之矣。
于虚无。黩武戎于要荒。特以大材略好资性。未有以与适于道者。遂乃驰心高远。从事征伐。以至祷祠角戏之具。殆若騃儿游嬉者然。诚以雄心大志。无所主着。莫可措置。不自觉其流入于荒怪诞妄。惜哉。余悲世之不察。乃与夫刚戾暴狠之秦皇而并称之也。迹其行事。虽若相类。而细究其心。固不可同年而语矣。得王媪及其男无故武赏赐巨万。皆封列侯。爱之欲富。赏赐之可矣。无功而侯。不义甚矣。卒之五侯颛恣。莽贼篡位。宣帝实启之矣。臣之于君。不择事而行义也。萧望之以左迁冯翊而即移病。此其器量褊狷。不免于及也。
韦玄成尝以让爵于兄。显名当世。则其节行有足多者。而及其为相也。顾乃周旋于石显牢鹿之间。一无所匡正。特一顽鄙无诟耻者耳。士之砥砺名节者。鲜克有终。亦可以少戒矣。
斩郅支单于。悬藁街十日。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悬。夫月令所言。非指此类。桀虏被讨。万里传首。其不可断以此例也明矣。匡鼎世号通经术。而乃引此为言。其见识之迂疏如是。夫夫如是。不能奉身于昏主佞臣之朝。甘与石显辈同列而上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9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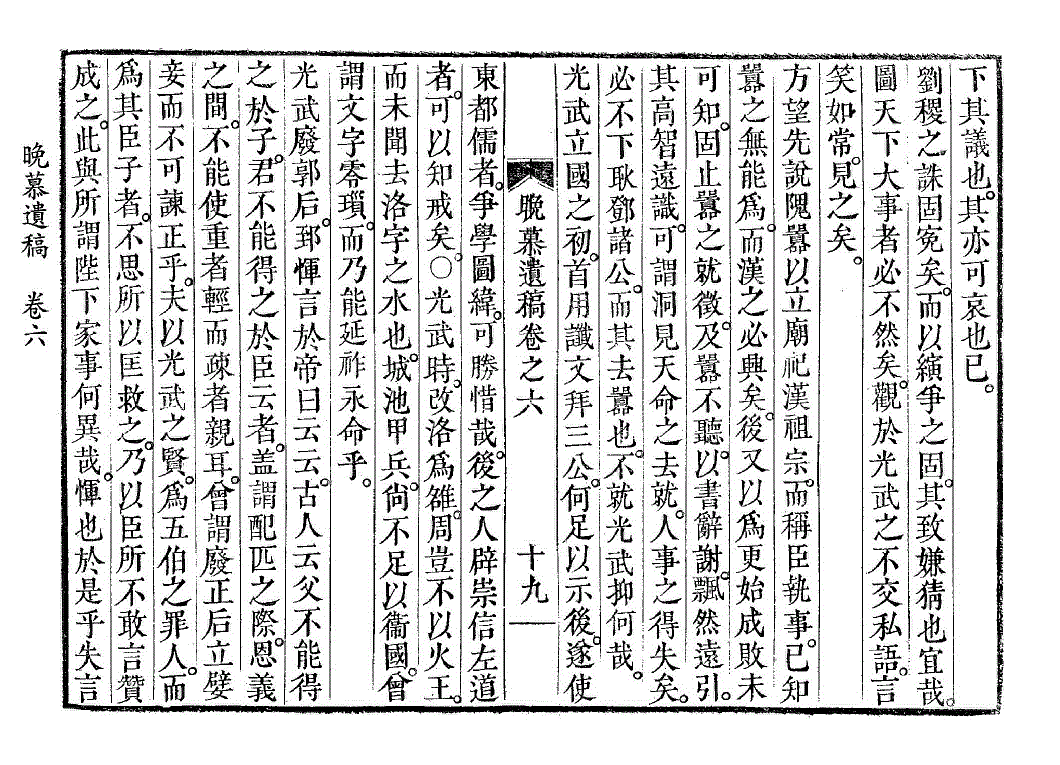 下其议也。其亦可哀也已。
下其议也。其亦可哀也已。刘稷之诛固冤矣。而以演争之固。其致嫌猜也宜哉。图天下大事者必不然矣。观于光武之不交私语。言笑如常。见之矣。
方望先说隗嚣以立庙祀汉祖宗。而称臣执事。已知嚣之无能为。而汉之必兴矣。后又以为更始成败未可知。固止嚣之就徵。及嚣不听。以书辞谢。飘然远引。其高智远识。可谓洞见天命之去就。人事之得失矣。必不下耿邓诸公。而其去嚣也。不就光武抑何哉。
光武立国之初。首用谶文拜三公。何足以示后。遂使东都儒者。争学图纬。可胜惜哉。后之人辟崇信左道者。可以知戒矣。○光武时。改洛为雒。周岂不以火王。而未闻去洛字之水也。城池甲兵。尚不足以卫国。曾谓文字零琐。而乃能延祚永命乎。
光武废郭后。郅恽言于帝曰云云。古人云父不能得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云者。盖谓配匹之际。恩义之间。不能使重者轻而疏者亲耳。曾谓废正后立嬖妾。而不可谏正乎。夫以光武之贤。为五伯之罪人。而为其臣子者。不思所以匡救之。乃以臣所不敢言赞成之。此与所谓陛下家事何异哉。恽也于是乎失言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29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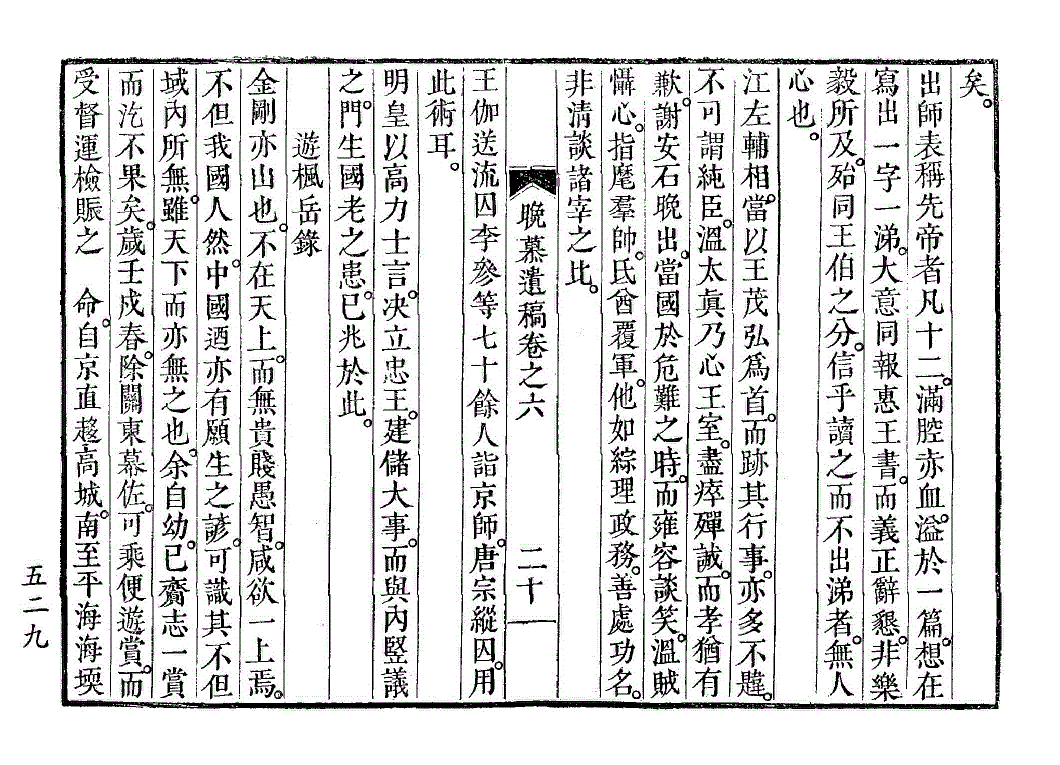 矣。
矣。出师表称先帝者凡十二。满腔赤血。溢于一篇。想在写出一字一涕。大意同报惠王书。而义正辞恳。非乐毅所及。殆同王伯之分。信乎读之而不出涕者。无人心也。
江左辅相。当以王茂弘为首。而迹其行事。亦多不韪。不可谓纯臣。温太真乃心王室。尽瘁殚诚。而孝犹有歉。谢安石晚出。当国于危难之时。而雍容谈笑。温贼慑心。指麾群帅。氐酋覆军。他如综理政务。善处功名。非清谈诸宰之比。
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诣京师。唐宗纵囚。用此术耳。
明皇以高力士言。决立忠王。建储大事。而与内竖议之。门生国老之患。已兆于此。
游枫岳录
金刚亦山也。不在天上。而无贵贱愚智。咸欲一上焉。不但我国人然。中国乃亦有愿生之谚。可识其不但域内所无。虽天下而亦无之也。余自幼。已赍志一赏而汔不果矣。岁壬戌春。除关东幕佐。可乘便游赏。而受督运检赈之 命。自京直趍高城。南至平海海堧
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0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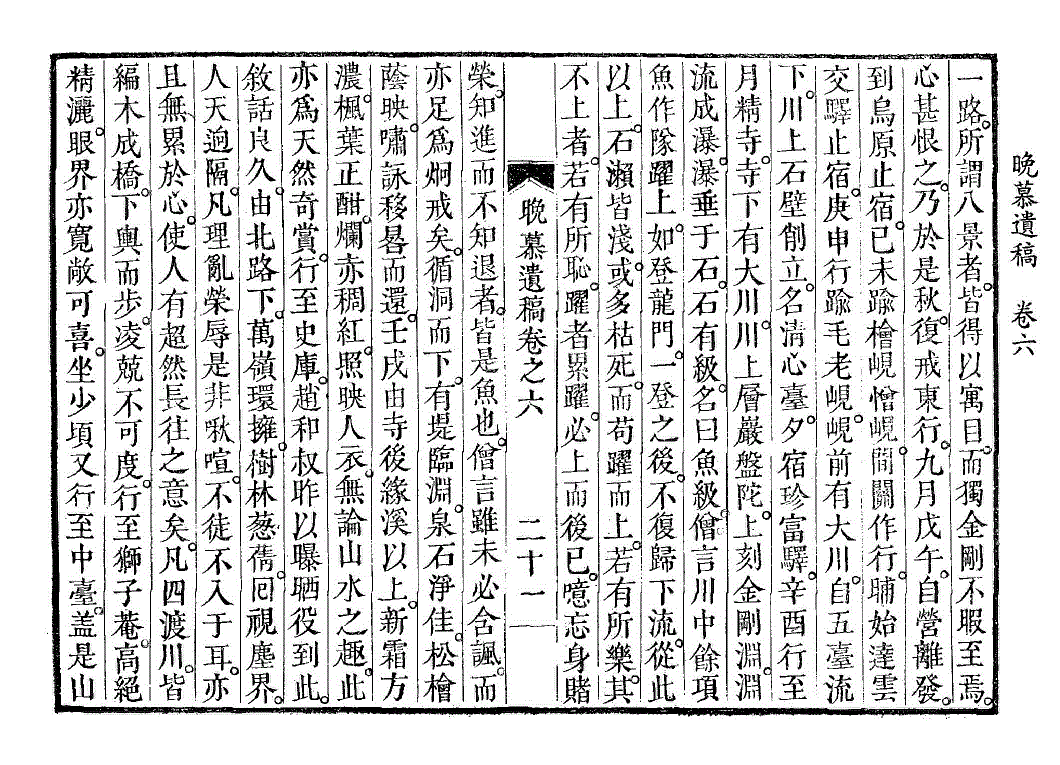 一路。所谓八景者。皆得以寓目。而独金刚不暇至焉。心甚恨之。乃于是秋。复戒东行。九月戊午。自营离发。到乌原止宿。己未踰桧岘憎岘。间关作行。晡始达云交驿止宿。庚申行踰毛老岘。岘前有大川。自五台流下。川上石壁削立。名清心台。夕宿珍富驿。辛酉行至月精寺。寺下有大川。川上层岩盘陀。上刻金刚渊。渊流成瀑。瀑垂于石。石有级。名曰鱼级。僧言川中馀项鱼作队跃上。如登龙门。一登之后。不复归下流。从此以上。石濑皆浅。或多枯死。而苟跃而上。若有所乐。其不上者。若有所耻。跃者累跃。必上而后已。噫忘身赌荣。知进而不知退者。皆是鱼也。僧言虽未必含讽。而亦足为炯戒矣。循洞而下。有堤临渊。泉石净佳。松桧荫映。啸咏移晷而还。壬戌由寺后缘溪以上。新霜方浓。枫叶正酣。烂赤稠红。照映人衣。无论山水之趣。此亦为天然奇赏。行至史库。赵和叔昨以曝晒役到此。叙话良久。由北路下。万岭环拥。树林葱茜。回视尘界。人天迥隔。凡理乱荣辱是非啾喧。不徒不入于耳。亦且无累于心。使人有超然长往之意矣。凡四渡川。皆编木成桥。下舆而步。凌兢不可度。行至狮子庵。高绝精洒。眼界亦宽敞可喜。坐少顷又行至中台。盖是山
一路。所谓八景者。皆得以寓目。而独金刚不暇至焉。心甚恨之。乃于是秋。复戒东行。九月戊午。自营离发。到乌原止宿。己未踰桧岘憎岘。间关作行。晡始达云交驿止宿。庚申行踰毛老岘。岘前有大川。自五台流下。川上石壁削立。名清心台。夕宿珍富驿。辛酉行至月精寺。寺下有大川。川上层岩盘陀。上刻金刚渊。渊流成瀑。瀑垂于石。石有级。名曰鱼级。僧言川中馀项鱼作队跃上。如登龙门。一登之后。不复归下流。从此以上。石濑皆浅。或多枯死。而苟跃而上。若有所乐。其不上者。若有所耻。跃者累跃。必上而后已。噫忘身赌荣。知进而不知退者。皆是鱼也。僧言虽未必含讽。而亦足为炯戒矣。循洞而下。有堤临渊。泉石净佳。松桧荫映。啸咏移晷而还。壬戌由寺后缘溪以上。新霜方浓。枫叶正酣。烂赤稠红。照映人衣。无论山水之趣。此亦为天然奇赏。行至史库。赵和叔昨以曝晒役到此。叙话良久。由北路下。万岭环拥。树林葱茜。回视尘界。人天迥隔。凡理乱荣辱是非啾喧。不徒不入于耳。亦且无累于心。使人有超然长往之意矣。凡四渡川。皆编木成桥。下舆而步。凌兢不可度。行至狮子庵。高绝精洒。眼界亦宽敞可喜。坐少顷又行至中台。盖是山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0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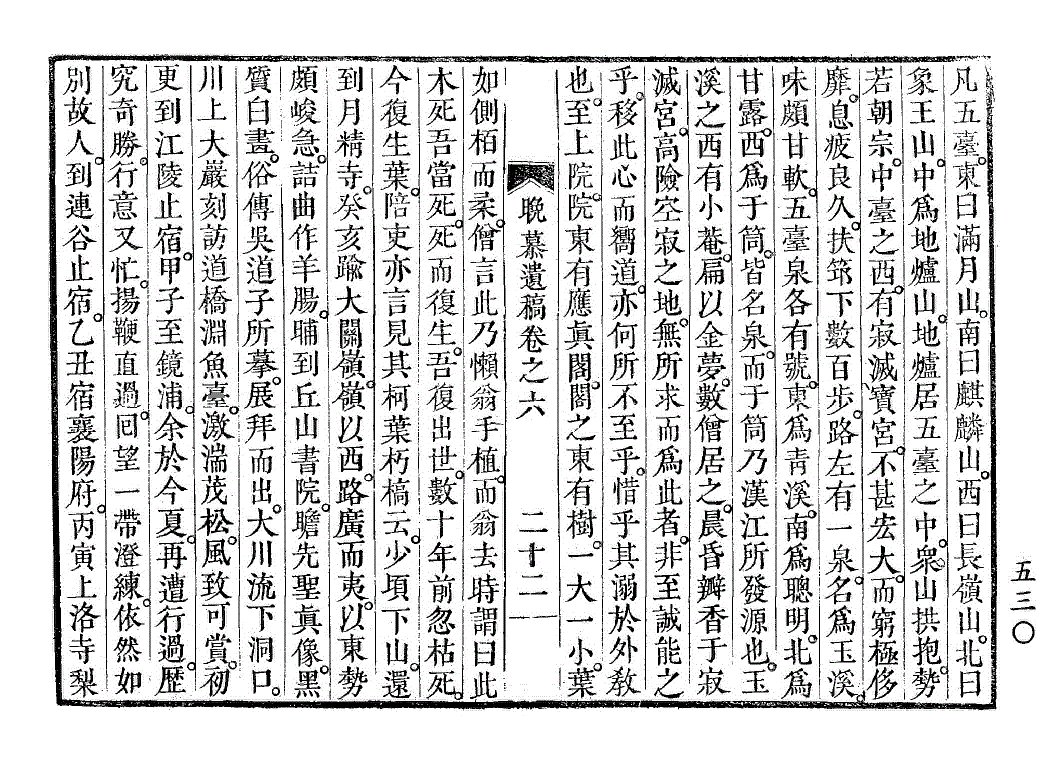 凡五台。东曰满月山。南曰麒麟山。西曰长岭山。北曰象王山。中为地炉山。地炉居五台之中。众山拱抱。势若朝宗。中台之西。有寂灭宝宫。不甚宏大。而穷极侈靡。息疲良久。扶筇下数百步。路左有一泉。名为玉溪。味颇甘软。五台泉各有号。东为青溪。南为聪明。北为甘露。西为于筒。皆名泉。而于筒乃汉江所发源也。玉溪之西有小庵。扁以金梦。数僧居之。晨昏瓣香于寂灭宫。高险空寂之地。无所求而为此者。非至诚能之乎。移此心而向道。亦何所不至乎。惜乎其溺于外教也。至上院。院东有应真阁。阁之东有树。一大一小。叶如侧柏而柔。僧言此乃懒翁手植。而翁去时谓曰此木死吾当死。死而复生。吾复出世。数十年前忽枯死。今复生叶。陪吏亦言见其柯叶朽槁云。少顷下山。还到月精寺。癸亥踰大关岭。岭以西。路广而夷。以东势颇峻急。诘曲作羊肠。晡到丘山书院。瞻先圣真像。黑质白画。俗传吴道子所摹。展拜而出。大川流下洞口。川上大岩刻访道桥渊鱼台。激湍茂松。风致可赏。初更到江陵止宿。甲子至镜浦。余于今夏。再遭行过。历究奇胜。行意又忙。扬鞭直过。回望一带澄练。依然如别故人。到连谷止宿。乙丑宿襄阳府。丙寅上洛寺梨
凡五台。东曰满月山。南曰麒麟山。西曰长岭山。北曰象王山。中为地炉山。地炉居五台之中。众山拱抱。势若朝宗。中台之西。有寂灭宝宫。不甚宏大。而穷极侈靡。息疲良久。扶筇下数百步。路左有一泉。名为玉溪。味颇甘软。五台泉各有号。东为青溪。南为聪明。北为甘露。西为于筒。皆名泉。而于筒乃汉江所发源也。玉溪之西有小庵。扁以金梦。数僧居之。晨昏瓣香于寂灭宫。高险空寂之地。无所求而为此者。非至诚能之乎。移此心而向道。亦何所不至乎。惜乎其溺于外教也。至上院。院东有应真阁。阁之东有树。一大一小。叶如侧柏而柔。僧言此乃懒翁手植。而翁去时谓曰此木死吾当死。死而复生。吾复出世。数十年前忽枯死。今复生叶。陪吏亦言见其柯叶朽槁云。少顷下山。还到月精寺。癸亥踰大关岭。岭以西。路广而夷。以东势颇峻急。诘曲作羊肠。晡到丘山书院。瞻先圣真像。黑质白画。俗传吴道子所摹。展拜而出。大川流下洞口。川上大岩刻访道桥渊鱼台。激湍茂松。风致可赏。初更到江陵止宿。甲子至镜浦。余于今夏。再遭行过。历究奇胜。行意又忙。扬鞭直过。回望一带澄练。依然如别故人。到连谷止宿。乙丑宿襄阳府。丙寅上洛寺梨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1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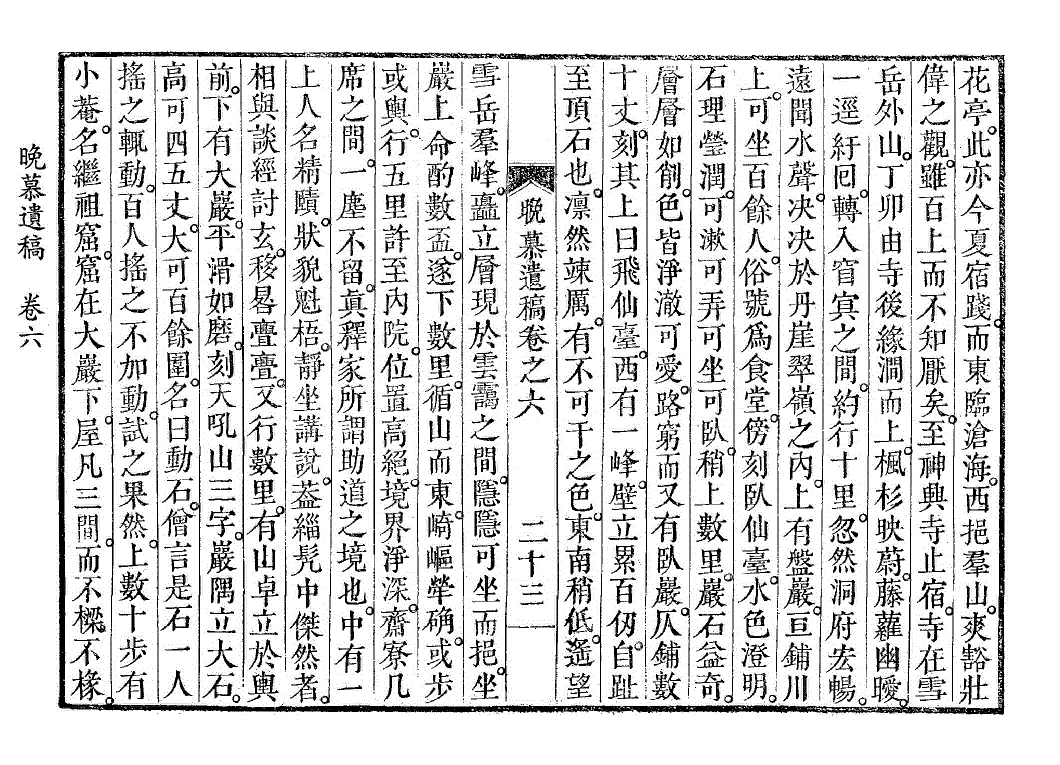 花亭。此亦今夏宿践。而东临沧海。西挹群山。爽豁壮伟之观。虽百上而不知厌矣。至神兴寺止宿。寺在雪岳外山。丁卯由寺后缘涧而上。枫杉映蔚。藤萝幽暧。一径纡回。转入窅冥之间。约行十里。忽然洞府宏畅。远闻水声。决决于丹崖翠岭之内。上有盘岩。亘铺川上。可坐百馀人。俗号为食堂。傍刻卧仙台。水色澄明。石理莹润。可漱可弄可坐可卧。稍上数里。岩石益奇。层层如削。色皆净澈可爱。路穷而又有卧岩。仄铺数十丈。刻其上曰飞仙台。西有一峰。壁立累百仞。自趾至顶石也。凛然竦厉。有不可干之色。东南稍低。遥望雪岳群峰。矗立层现于云霭之间。隐隐可坐而挹。坐岩上命酌数杯。遂下数里。循山而东。崎岖荦确。或步或舆。行五里许至内院。位置高绝。境界净深。斋寮几席之间。一尘不留。真释家所谓助道之境也。中有一上人名精赜。状貌魁梧。静坐讲说。盖缁髡中杰然者。相与谈经讨玄。移晷亹亹。又行数里。有山卓立于舆前。下有大岩。平滑如磨。刻天吼山三字。岩隅立大石。高可四五丈。大可百馀围。名曰动石。僧言是石一人摇之辄动。百人摇之不加动。试之果然。上数十步有小庵。名继祖窟。窟在大岩下。屋凡三间。而不梁不椽。
花亭。此亦今夏宿践。而东临沧海。西挹群山。爽豁壮伟之观。虽百上而不知厌矣。至神兴寺止宿。寺在雪岳外山。丁卯由寺后缘涧而上。枫杉映蔚。藤萝幽暧。一径纡回。转入窅冥之间。约行十里。忽然洞府宏畅。远闻水声。决决于丹崖翠岭之内。上有盘岩。亘铺川上。可坐百馀人。俗号为食堂。傍刻卧仙台。水色澄明。石理莹润。可漱可弄可坐可卧。稍上数里。岩石益奇。层层如削。色皆净澈可爱。路穷而又有卧岩。仄铺数十丈。刻其上曰飞仙台。西有一峰。壁立累百仞。自趾至顶石也。凛然竦厉。有不可干之色。东南稍低。遥望雪岳群峰。矗立层现于云霭之间。隐隐可坐而挹。坐岩上命酌数杯。遂下数里。循山而东。崎岖荦确。或步或舆。行五里许至内院。位置高绝。境界净深。斋寮几席之间。一尘不留。真释家所谓助道之境也。中有一上人名精赜。状貌魁梧。静坐讲说。盖缁髡中杰然者。相与谈经讨玄。移晷亹亹。又行数里。有山卓立于舆前。下有大岩。平滑如磨。刻天吼山三字。岩隅立大石。高可四五丈。大可百馀围。名曰动石。僧言是石一人摇之辄动。百人摇之不加动。试之果然。上数十步有小庵。名继祖窟。窟在大岩下。屋凡三间。而不梁不椽。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1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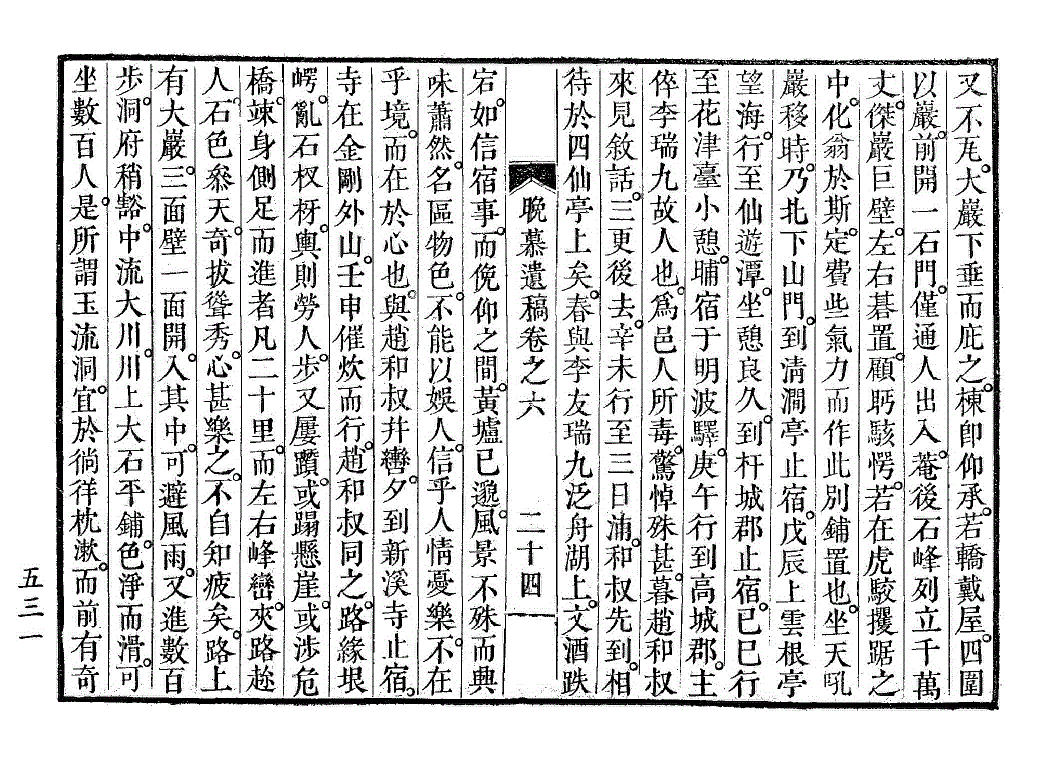 又不瓦。大岩下垂而庇之。栋即仰承。若轿戴屋。四围以岩。前开一石门。仅通人出入。庵后石峰列立千万丈。杰岩巨壁。左右棋置。顾眄骇愕。若在虎駮攫踞之中。化翁于斯。定费些气力而作此别铺置也。坐天吼岩移时。乃北下山门。到清涧亭止宿。戊辰上云根亭望海。行至仙游潭。坐憩良久。到杆城郡止宿。己巳行至花津台小憩。晡宿于明波驿。庚午行到高城郡。主倅李瑞九故人也。为邑人所毒。惊悼殊甚。暮赵和叔来见叙话。三更后去。辛未行至三日浦。和叔先到。相待于四仙亭上矣。春与李友瑞九泛舟湖上。文酒跌宕。如信宿事。而俛仰之间。黄垆已邈。风景不殊而兴味萧然。名区物色。不能以娱人。信乎人情忧乐。不在乎境。而在于心也。与赵和叔并辔。夕到新溪寺止宿。寺在金刚外山。壬申催炊而行。赵和叔同之。路缘垠崿。乱石杈枒。舆则劳人。步又屡踬。或蹋悬崖。或涉危桥。竦身侧足而进者凡二十里。而左右峰峦。夹路趁人。石色参天。奇拔耸秀。心甚乐之。不自知疲矣。路上有大岩。三面壁一面开。入其中。可避风雨。又进数百步。洞府稍豁。中流大川。川上大石平铺。色净而滑。可坐数百人。是所谓玉流洞。宜于徜徉枕漱。而前有奇
又不瓦。大岩下垂而庇之。栋即仰承。若轿戴屋。四围以岩。前开一石门。仅通人出入。庵后石峰列立千万丈。杰岩巨壁。左右棋置。顾眄骇愕。若在虎駮攫踞之中。化翁于斯。定费些气力而作此别铺置也。坐天吼岩移时。乃北下山门。到清涧亭止宿。戊辰上云根亭望海。行至仙游潭。坐憩良久。到杆城郡止宿。己巳行至花津台小憩。晡宿于明波驿。庚午行到高城郡。主倅李瑞九故人也。为邑人所毒。惊悼殊甚。暮赵和叔来见叙话。三更后去。辛未行至三日浦。和叔先到。相待于四仙亭上矣。春与李友瑞九泛舟湖上。文酒跌宕。如信宿事。而俛仰之间。黄垆已邈。风景不殊而兴味萧然。名区物色。不能以娱人。信乎人情忧乐。不在乎境。而在于心也。与赵和叔并辔。夕到新溪寺止宿。寺在金刚外山。壬申催炊而行。赵和叔同之。路缘垠崿。乱石杈枒。舆则劳人。步又屡踬。或蹋悬崖。或涉危桥。竦身侧足而进者凡二十里。而左右峰峦。夹路趁人。石色参天。奇拔耸秀。心甚乐之。不自知疲矣。路上有大岩。三面壁一面开。入其中。可避风雨。又进数百步。洞府稍豁。中流大川。川上大石平铺。色净而滑。可坐数百人。是所谓玉流洞。宜于徜徉枕漱。而前有奇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2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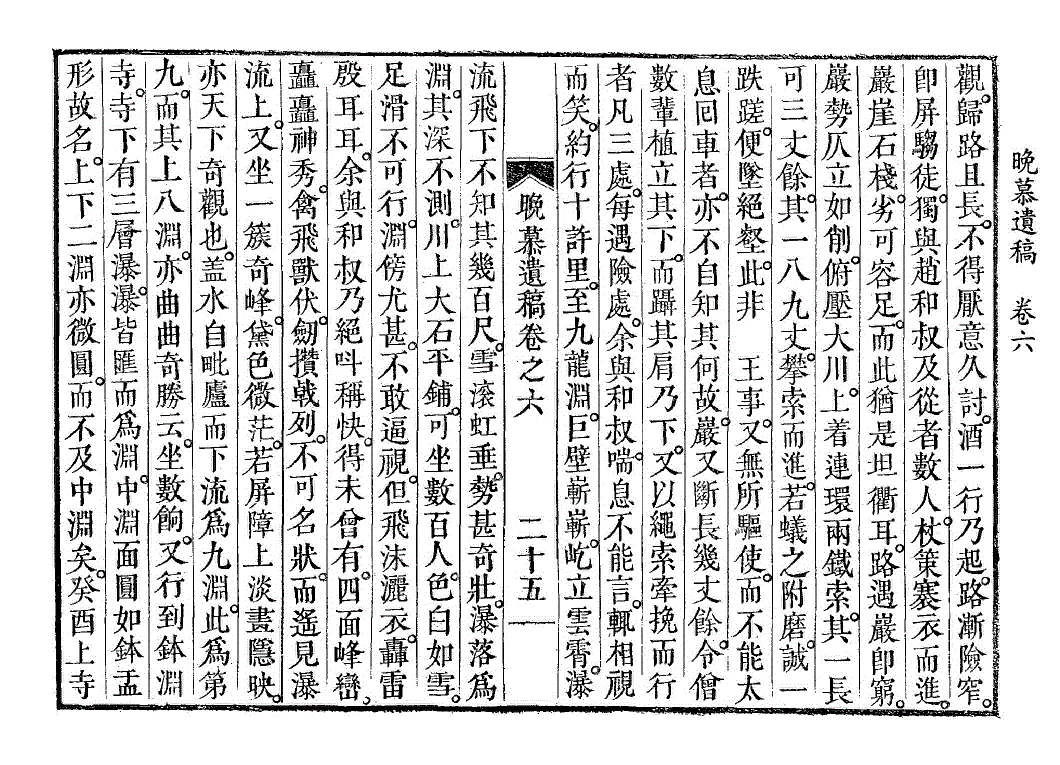 观。归路且长。不得厌意久讨。酒一行乃起。路渐险窄。即屏驺徒。独与赵和叔及从者数人。杖策褰衣而进。岩崖石栈。劣可容足。而此犹是坦衢耳。路遇岩即穷。岩势仄立如削。俯压大川。上着连环两铁索。其一长可三丈馀。其一八九丈。攀索而进。若蚁之附磨。诚一跌蹉。便坠绝壑。此非 王事。又无所驱使。而不能太息回车者。亦不自知其何故。岩又断长几丈馀。令僧数辈植立其下。而蹑其肩乃下。又以绳索牵挽而行者凡三处。每遇险处。余与和叔。喘息不能言。辄相视而笑。约行十许里。至九龙渊。巨壁崭崭。屹立云霄。瀑流飞下不知其几百尺。雪滚虹垂。势甚奇壮。瀑落为渊。其深不测。川上大石平铺。可坐数百人。色白如雪。足滑不可行。渊傍尤甚。不敢逼视。但飞沫洒衣。轰雷殷耳耳。余与和叔乃绝叫称快。得未曾有。四面峰峦。矗矗神秀。禽飞兽伏。剑攒戟列。不可名状。而遥见瀑流上。又坐一簇奇峰。黛色微茫。若屏障上淡画隐映。亦天下奇观也。盖水自毗庐(一作卢)而下流为九渊。此为第九。而其上八渊。亦曲曲奇胜云。坐数饷。又行到钵渊寺。寺下有三层瀑。瀑皆汇而为渊。中渊面圆如钵盂形故名。上下二渊亦微圆。而不及中渊矣。癸酉上寺
观。归路且长。不得厌意久讨。酒一行乃起。路渐险窄。即屏驺徒。独与赵和叔及从者数人。杖策褰衣而进。岩崖石栈。劣可容足。而此犹是坦衢耳。路遇岩即穷。岩势仄立如削。俯压大川。上着连环两铁索。其一长可三丈馀。其一八九丈。攀索而进。若蚁之附磨。诚一跌蹉。便坠绝壑。此非 王事。又无所驱使。而不能太息回车者。亦不自知其何故。岩又断长几丈馀。令僧数辈植立其下。而蹑其肩乃下。又以绳索牵挽而行者凡三处。每遇险处。余与和叔。喘息不能言。辄相视而笑。约行十许里。至九龙渊。巨壁崭崭。屹立云霄。瀑流飞下不知其几百尺。雪滚虹垂。势甚奇壮。瀑落为渊。其深不测。川上大石平铺。可坐数百人。色白如雪。足滑不可行。渊傍尤甚。不敢逼视。但飞沫洒衣。轰雷殷耳耳。余与和叔乃绝叫称快。得未曾有。四面峰峦。矗矗神秀。禽飞兽伏。剑攒戟列。不可名状。而遥见瀑流上。又坐一簇奇峰。黛色微茫。若屏障上淡画隐映。亦天下奇观也。盖水自毗庐(一作卢)而下流为九渊。此为第九。而其上八渊。亦曲曲奇胜云。坐数饷。又行到钵渊寺。寺下有三层瀑。瀑皆汇而为渊。中渊面圆如钵盂形故名。上下二渊亦微圆。而不及中渊矣。癸酉上寺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2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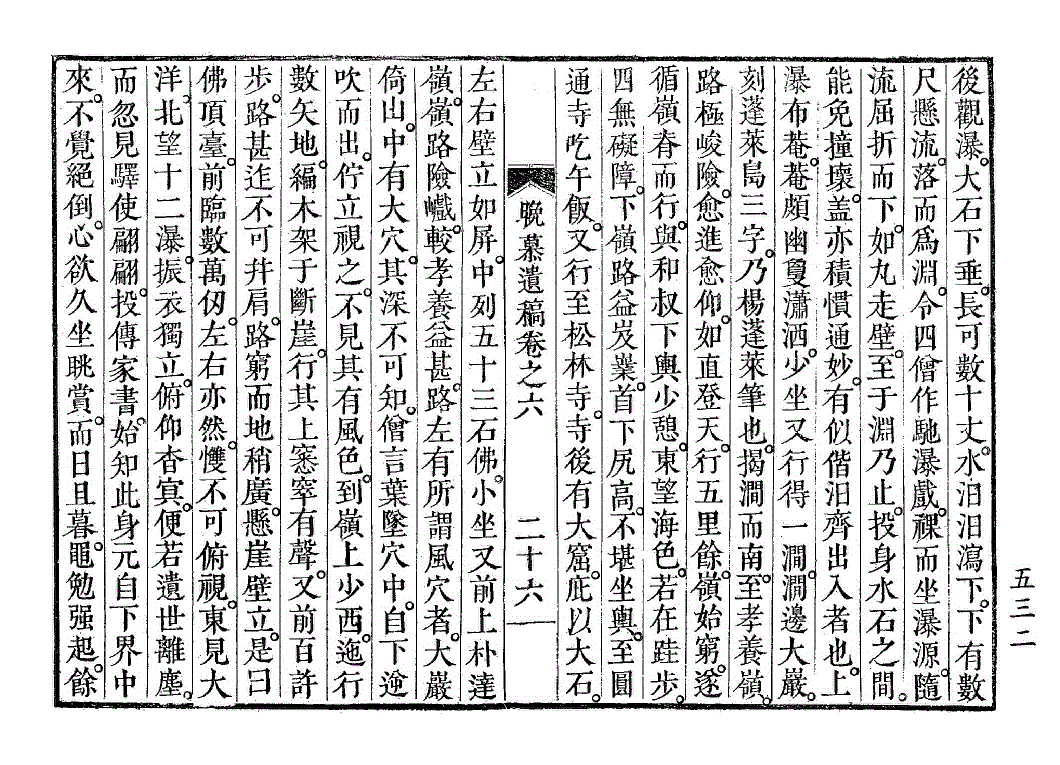 后观瀑。大石下垂。长可数十丈。水汩汩泻下。下有数尺悬流。落而为渊。令四僧作驰瀑戏。裸而坐瀑源。随流屈折而下。如丸走壁。至于渊乃止。投身水石之间。能免撞坏。盖亦积惯通妙。有似偕汩齐出入者也。上瀑布庵。庵颇幽夐潇洒。少坐又行得一涧。涧边大岩。刻蓬莱岛三字。乃杨蓬莱笔也。揭涧而南。至孝养岭。路极峻险。愈进愈仰。如直登天。行五里馀。岭始穷。遂循岭脊而行。与和叔下舆少憩。东望海色。若在跬步。四无碍障。下岭路益岌嶪。首下尻高。不堪坐舆。至圆通寺吃午饭。又行至松林寺。寺后有大窟。庇以大石。左右壁立如屏。中列五十三石佛。小坐又前上朴达岭。岭路险巇。较孝养益甚。路左有所谓风穴者。大岩倚山。中有大穴。其深不可知。僧言叶坠穴中。自下逆吹而出。伫立视之。不见其有风色。到岭上少西。迤行数矢地。编木架于断崖。行其上窸窣有声。又前百许步。路甚迮不可并肩。路穷而地稍广。悬崖壁立。是曰佛顶台。前临数万仞。左右亦然。𢥠不可俯视。东见大洋。北望十二瀑。振衣独立。俯仰杳冥。便若遗世离尘。而忽见驿使翩翩。投传家书。始知此身元自下界中来。不觉绝倒。心欲久坐眺赏。而日且暮。黾勉强起。馀
后观瀑。大石下垂。长可数十丈。水汩汩泻下。下有数尺悬流。落而为渊。令四僧作驰瀑戏。裸而坐瀑源。随流屈折而下。如丸走壁。至于渊乃止。投身水石之间。能免撞坏。盖亦积惯通妙。有似偕汩齐出入者也。上瀑布庵。庵颇幽夐潇洒。少坐又行得一涧。涧边大岩。刻蓬莱岛三字。乃杨蓬莱笔也。揭涧而南。至孝养岭。路极峻险。愈进愈仰。如直登天。行五里馀。岭始穷。遂循岭脊而行。与和叔下舆少憩。东望海色。若在跬步。四无碍障。下岭路益岌嶪。首下尻高。不堪坐舆。至圆通寺吃午饭。又行至松林寺。寺后有大窟。庇以大石。左右壁立如屏。中列五十三石佛。小坐又前上朴达岭。岭路险巇。较孝养益甚。路左有所谓风穴者。大岩倚山。中有大穴。其深不可知。僧言叶坠穴中。自下逆吹而出。伫立视之。不见其有风色。到岭上少西。迤行数矢地。编木架于断崖。行其上窸窣有声。又前百许步。路甚迮不可并肩。路穷而地稍广。悬崖壁立。是曰佛顶台。前临数万仞。左右亦然。𢥠不可俯视。东见大洋。北望十二瀑。振衣独立。俯仰杳冥。便若遗世离尘。而忽见驿使翩翩。投传家书。始知此身元自下界中来。不觉绝倒。心欲久坐眺赏。而日且暮。黾勉强起。馀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3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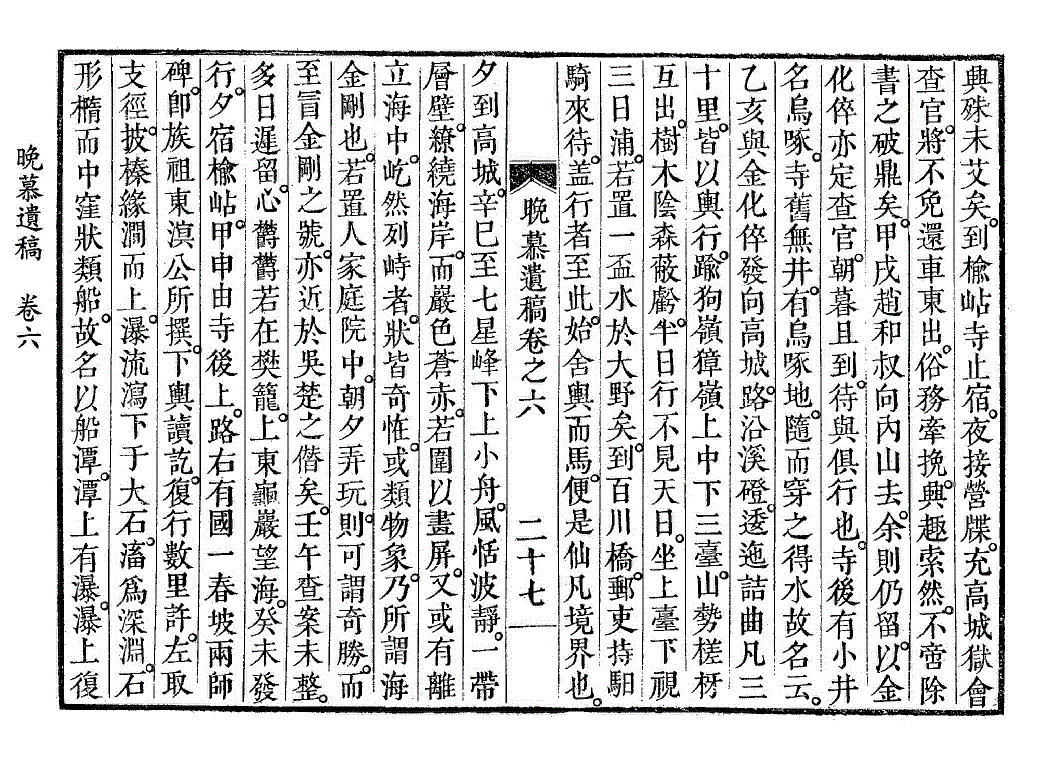 兴殊未艾矣。到榆岾寺止宿。夜接营牒。充高城狱会查官。将不免还车东出。俗务牵挽。兴趣索然。不啻除书之破鼎矣。甲戌赵和叔向内山去。余则仍留。以金化倅亦定查官。朝暮且到。待与俱行也。寺后有小井名乌啄。寺旧无井。有乌啄地。随而穿之得水故名云。乙亥与金化倅发向高城。路沿溪磴。逶迤诘曲凡三十里。皆以舆行。踰狗岭獐岭上中下三台。山势槎枒互出。树木阴森蔽亏。半日行不见天日。坐上台下视三日浦。若置一杯水于大野矣。到百川桥。邮吏持驲骑来待。盖行者至此。始舍舆而马。便是仙凡境界也。夕到高城。辛巳至七星峰下上小舟。风恬波静。一带层壁。缭绕海岸。而岩色苍赤。若围以画屏。又或有离立海中。屹然列峙者。状皆奇怪。或类物象。乃所谓海金刚也。若置人家庭院中。朝夕弄玩。则可谓奇胜。而至冒金刚之号。亦近于吴楚之僭矣。壬午查案未整。多日迟留。心郁郁若在樊笼。上东龟岩望海。癸未发行。夕宿榆岾。甲申由寺后上。路右有国一春坡两师碑。即族祖东溟公所撰。下舆读讫。复行数里许。左取支径。披榛缘涧而上。瀑流泻下于大石。滀为深渊。石形椭而中洼状类船。故名以船潭。潭上有瀑。瀑上复
兴殊未艾矣。到榆岾寺止宿。夜接营牒。充高城狱会查官。将不免还车东出。俗务牵挽。兴趣索然。不啻除书之破鼎矣。甲戌赵和叔向内山去。余则仍留。以金化倅亦定查官。朝暮且到。待与俱行也。寺后有小井名乌啄。寺旧无井。有乌啄地。随而穿之得水故名云。乙亥与金化倅发向高城。路沿溪磴。逶迤诘曲凡三十里。皆以舆行。踰狗岭獐岭上中下三台。山势槎枒互出。树木阴森蔽亏。半日行不见天日。坐上台下视三日浦。若置一杯水于大野矣。到百川桥。邮吏持驲骑来待。盖行者至此。始舍舆而马。便是仙凡境界也。夕到高城。辛巳至七星峰下上小舟。风恬波静。一带层壁。缭绕海岸。而岩色苍赤。若围以画屏。又或有离立海中。屹然列峙者。状皆奇怪。或类物象。乃所谓海金刚也。若置人家庭院中。朝夕弄玩。则可谓奇胜。而至冒金刚之号。亦近于吴楚之僭矣。壬午查案未整。多日迟留。心郁郁若在樊笼。上东龟岩望海。癸未发行。夕宿榆岾。甲申由寺后上。路右有国一春坡两师碑。即族祖东溟公所撰。下舆读讫。复行数里许。左取支径。披榛缘涧而上。瀑流泻下于大石。滀为深渊。石形椭而中洼状类船。故名以船潭。潭上有瀑。瀑上复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3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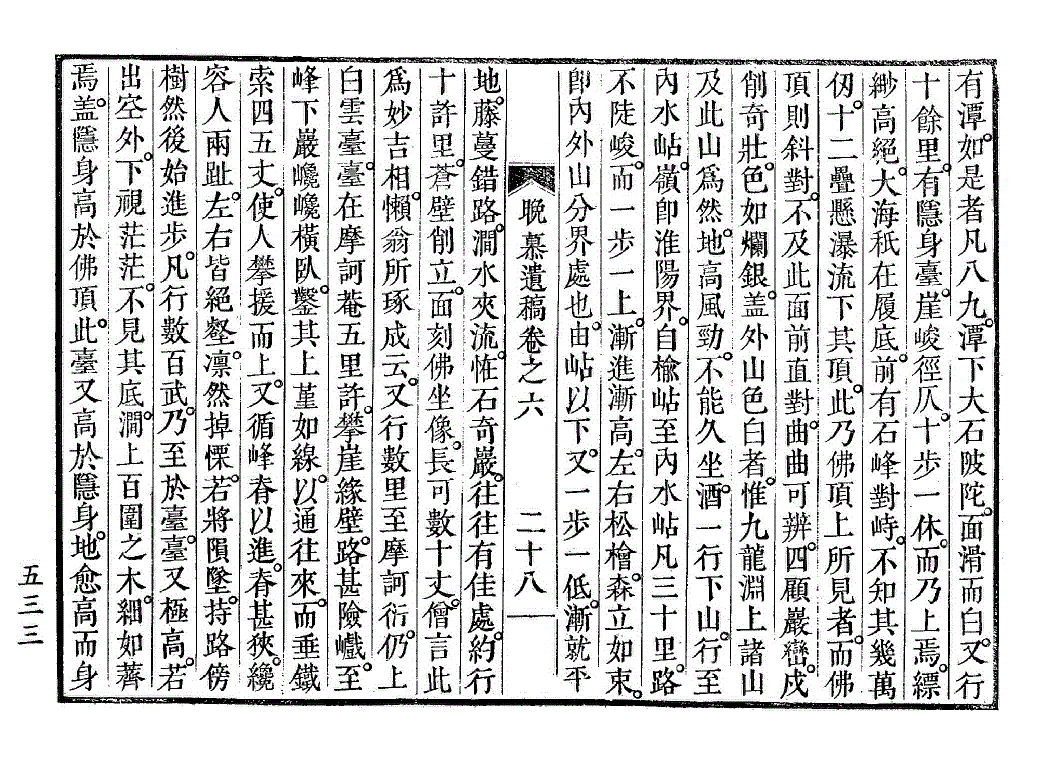 有潭。如是者凡八九。潭下大石陂陀。面滑而白。又行十馀里。有隐身台。崖峻径仄。十步一休。而乃上焉。缥缈高绝。大海秖在履底。前有石峰对峙。不知其几万仞。十二叠悬瀑流下其顶。此乃佛顶上所见者。而佛顶则斜对。不及此面前直对。曲曲可辨。四顾岩峦。戌削奇壮。色如烂银。盖外山色白者。惟九龙渊上诸山及此山为然。地高风劲。不能久坐。酒一行下山。行至内水岾。岭即淮阳界。自榆岾至内水岾凡三十里。路不陡峻。而一步一上。渐进渐高。左右松桧。森立如束。即内外山分界处也。由岾以下。又一步一低。渐就平地。藤蔓错路。涧水夹流。怪石奇岩。往往有佳处。约行十许里。苍壁削立。面刻佛坐像。长可数十丈。僧言此为妙吉相。懒翁所琢成云。又行数里至摩诃衍。仍上白云台。台在摩诃庵五里许。攀崖缘壁。路甚险巇。至峰下岩巉巉横卧。凿其上堇如线。以通往来。而垂铁索四五丈。使人攀援而上。又循峰脊以进。脊甚狭。才容人两趾。左右皆绝壑。凛然掉慄。若将陨坠。持路傍树然后始进步。凡行数百武。乃至于台。台又极高。若出空外。下视茫茫。不见其底。涧上百围之木。细如荠焉。盖隐身高于佛顶。此台又高于隐身。地愈高而身
有潭。如是者凡八九。潭下大石陂陀。面滑而白。又行十馀里。有隐身台。崖峻径仄。十步一休。而乃上焉。缥缈高绝。大海秖在履底。前有石峰对峙。不知其几万仞。十二叠悬瀑流下其顶。此乃佛顶上所见者。而佛顶则斜对。不及此面前直对。曲曲可辨。四顾岩峦。戌削奇壮。色如烂银。盖外山色白者。惟九龙渊上诸山及此山为然。地高风劲。不能久坐。酒一行下山。行至内水岾。岭即淮阳界。自榆岾至内水岾凡三十里。路不陡峻。而一步一上。渐进渐高。左右松桧。森立如束。即内外山分界处也。由岾以下。又一步一低。渐就平地。藤蔓错路。涧水夹流。怪石奇岩。往往有佳处。约行十许里。苍壁削立。面刻佛坐像。长可数十丈。僧言此为妙吉相。懒翁所琢成云。又行数里至摩诃衍。仍上白云台。台在摩诃庵五里许。攀崖缘壁。路甚险巇。至峰下岩巉巉横卧。凿其上堇如线。以通往来。而垂铁索四五丈。使人攀援而上。又循峰脊以进。脊甚狭。才容人两趾。左右皆绝壑。凛然掉慄。若将陨坠。持路傍树然后始进步。凡行数百武。乃至于台。台又极高。若出空外。下视茫茫。不见其底。涧上百围之木。细如荠焉。盖隐身高于佛顶。此台又高于隐身。地愈高而身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4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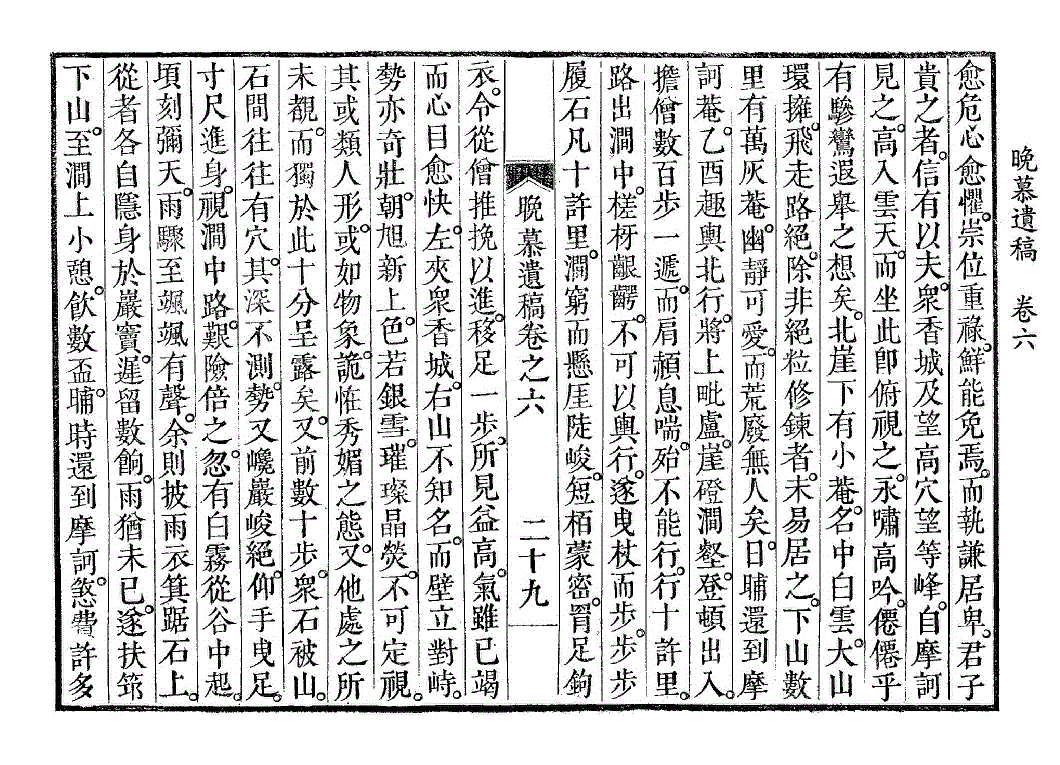 愈危心愈惧。崇位重禄。鲜能免焉。而执谦居卑。君子贵之者。信有以夫。众香城及望高穴望等峰。自摩诃见之。高入云天。而坐此即俯视之。永啸高吟。仙仙乎有骖鸾遐举之想矣。北崖下有小庵。名中白云。大山环拥。飞走路绝。除非绝粒修鍊者。未易居之。下山数里有万灰庵。幽静可爱。而荒废无人矣。日晡还到摩诃庵。乙酉趣舆北行。将上毗卢。崖磴涧壑。登顿出入。担僧数百步一递。而肩赪息喘。殆不能行。行十许里。路出涧中。槎枒龈腭。不可以舆行。遂曳杖而步。步步履石凡十许里。涧穷而悬厓陡峻。短柏蒙密。罥足钩衣。令从僧推挽以进。移足一步。所见益高。气虽已竭而心目愈快。左夹众香城。右山不知名。而壁立对峙。势亦奇壮。朝旭新上。色若银雪。璀璨晶荧。不可定视。其或类人形。或如物象。诡怪秀媚之态。又他处之所未睹。而独于此十分呈露矣。又前数十步。众石被山。石间往往有穴。其深不测。势又巉岩峻绝。仰手曳足。寸尺进身。视涧中路。艰险倍之。忽有白雾从谷中起。顷刻弥天。雨骤至飒飒有声。余则披雨衣箕踞石上。从者各自隐身于岩窦。迟留数饷。雨犹未已。遂扶筇下山。至涧上小憩。饮数杯。晡时还到摩诃。煞费许多
愈危心愈惧。崇位重禄。鲜能免焉。而执谦居卑。君子贵之者。信有以夫。众香城及望高穴望等峰。自摩诃见之。高入云天。而坐此即俯视之。永啸高吟。仙仙乎有骖鸾遐举之想矣。北崖下有小庵。名中白云。大山环拥。飞走路绝。除非绝粒修鍊者。未易居之。下山数里有万灰庵。幽静可爱。而荒废无人矣。日晡还到摩诃庵。乙酉趣舆北行。将上毗卢。崖磴涧壑。登顿出入。担僧数百步一递。而肩赪息喘。殆不能行。行十许里。路出涧中。槎枒龈腭。不可以舆行。遂曳杖而步。步步履石凡十许里。涧穷而悬厓陡峻。短柏蒙密。罥足钩衣。令从僧推挽以进。移足一步。所见益高。气虽已竭而心目愈快。左夹众香城。右山不知名。而壁立对峙。势亦奇壮。朝旭新上。色若银雪。璀璨晶荧。不可定视。其或类人形。或如物象。诡怪秀媚之态。又他处之所未睹。而独于此十分呈露矣。又前数十步。众石被山。石间往往有穴。其深不测。势又巉岩峻绝。仰手曳足。寸尺进身。视涧中路。艰险倍之。忽有白雾从谷中起。顷刻弥天。雨骤至飒飒有声。余则披雨衣箕踞石上。从者各自隐身于岩窦。迟留数饷。雨犹未已。遂扶筇下山。至涧上小憩。饮数杯。晡时还到摩诃。煞费许多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4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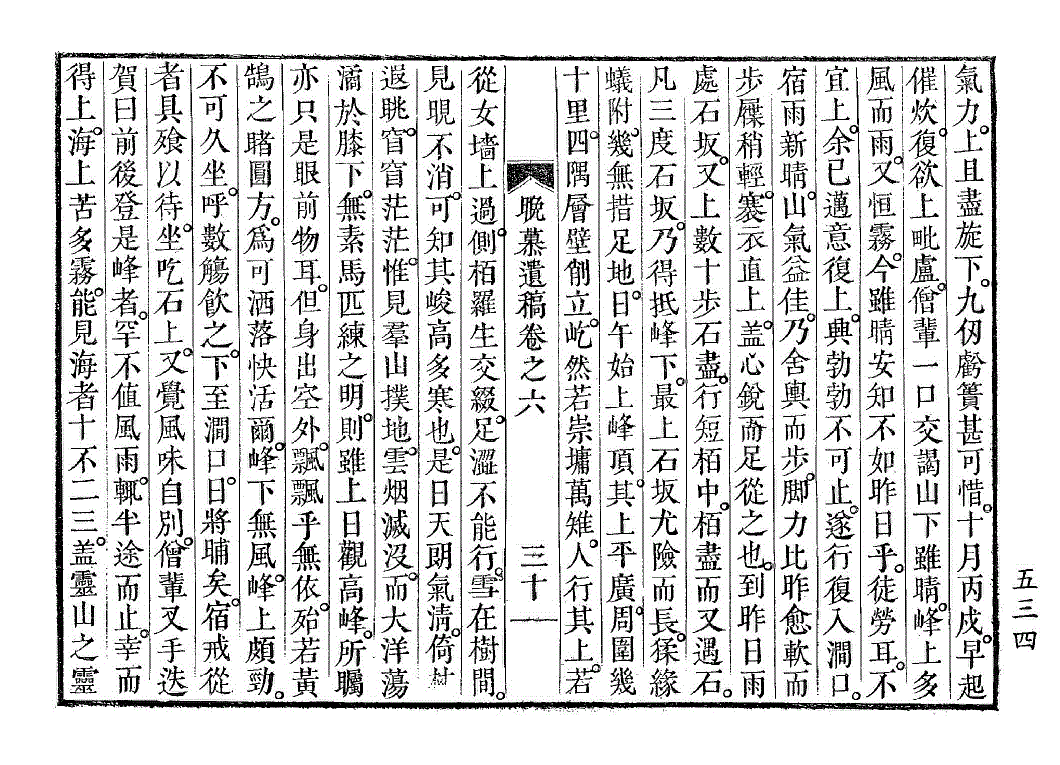 气力。上且尽旋下。九仞亏篑甚可惜。十月丙戌。早起催炊。复欲上毗卢。僧辈一口交谒山下虽晴。峰上多风而雨。又恒雾。今虽晴安知不如昨日乎。徒劳耳。不宜上。余已迈意复上。兴勃勃不可止。遂行复入涧口。宿雨新晴。山气益佳。乃舍舆而步。脚力比昨愈软而步屧稍轻。褰衣直上。盖心锐而足从之也。到昨日雨处石坂。又上数十步石尽。行短柏中。柏尽而又遇石。凡三度石坂。乃得抵峰下。最上石坂尤险而长。猱缘蚁附。几无措足地。日午始上峰顶。其上平广。周围几十里。四隅层壁削立。屹然若崇墉万雉。人行其上。若从女墙上过。侧柏罗生交缀。足涩不能行。雪在树间。见晛不消。可知其峻高多寒也。是日天朗气清。倚杖遐眺。窅窅茫茫。惟见群山扑地。云烟灭没。而大洋荡潏于膝下。无素马匹练之明。则虽上日观高峰。所瞩亦只是眼前物耳。但身出空外。飘飘乎无依。殆若黄鹄之睹圆方。为可洒落快活尔。峰下无风。峰上颇劲。不可久坐。呼数觞饮之。下至涧口。日将晡矣。宿戒从者具飧以待。坐吃石上。又觉风味自别。僧辈叉手迭贺曰前后登是峰者。罕不值风雨。辄半途而止。幸而得上。海上苦多雾。能见海者十不二三。盖灵山之灵
气力。上且尽旋下。九仞亏篑甚可惜。十月丙戌。早起催炊。复欲上毗卢。僧辈一口交谒山下虽晴。峰上多风而雨。又恒雾。今虽晴安知不如昨日乎。徒劳耳。不宜上。余已迈意复上。兴勃勃不可止。遂行复入涧口。宿雨新晴。山气益佳。乃舍舆而步。脚力比昨愈软而步屧稍轻。褰衣直上。盖心锐而足从之也。到昨日雨处石坂。又上数十步石尽。行短柏中。柏尽而又遇石。凡三度石坂。乃得抵峰下。最上石坂尤险而长。猱缘蚁附。几无措足地。日午始上峰顶。其上平广。周围几十里。四隅层壁削立。屹然若崇墉万雉。人行其上。若从女墙上过。侧柏罗生交缀。足涩不能行。雪在树间。见晛不消。可知其峻高多寒也。是日天朗气清。倚杖遐眺。窅窅茫茫。惟见群山扑地。云烟灭没。而大洋荡潏于膝下。无素马匹练之明。则虽上日观高峰。所瞩亦只是眼前物耳。但身出空外。飘飘乎无依。殆若黄鹄之睹圆方。为可洒落快活尔。峰下无风。峰上颇劲。不可久坐。呼数觞饮之。下至涧口。日将晡矣。宿戒从者具飧以待。坐吃石上。又觉风味自别。僧辈叉手迭贺曰前后登是峰者。罕不值风雨。辄半途而止。幸而得上。海上苦多雾。能见海者十不二三。盖灵山之灵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5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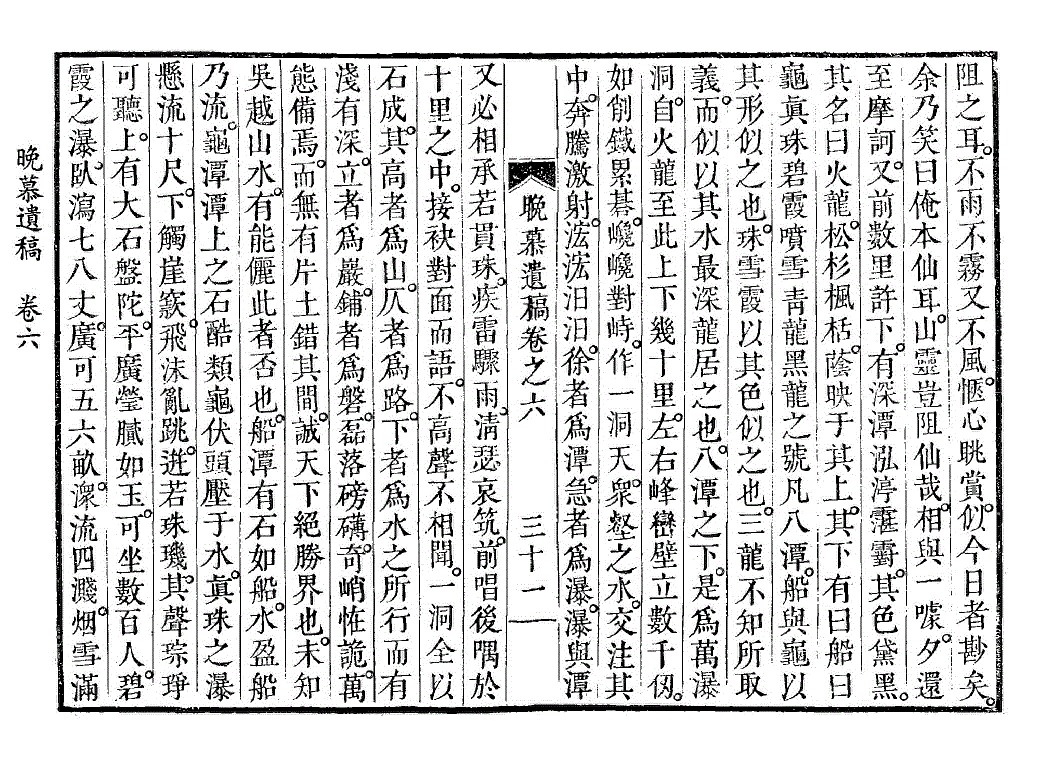 阻之耳。不雨不雾又不风。惬心眺赏。似今日者鲜矣。余乃笑曰俺本仙耳。山灵岂阻仙哉。相与一噱。夕还至摩诃。又前数里许下。有深潭泓渟霮䨴。其色黛黑。其名曰火龙。松杉枫栝。荫映于其上。其下有曰船曰龟真珠碧霞喷雪青龙黑龙之号凡八潭。船与龟以其形似之也。珠雪霞以其色似之也。三龙不知所取义。而似以其水最深龙居之也。八潭之下。是为万瀑洞。自火龙至此上下几十里。左右峰峦壁立数千仞。如削铁累棋。巉巉对峙。作一洞天。众壑之水。交注其中。奔腾激射。浤浤汩汩。徐者为潭。急者为瀑。瀑与潭又必相承若贯珠。疾雷骤雨。清瑟哀筑。前唱后喁于十里之中。接袂对面而语。不高声不相闻。一洞全以石成。其高者为山。仄者为路。下者为水之所行而有浅有深。立者为岩。铺者为磐。磊落磅礴。奇峭怪诡。万态备焉。而无有片土错其间。诚天下绝胜界也。未知吴越山水。有能俪此者否也。船潭有石如船。水盈船乃流。龟潭潭上之石酷类龟伏头压于水。真珠之瀑悬流十尺。下触崖窾。飞沫乱跳。迸若珠玑。其声琮琤可听。上有大石盘陀。平广莹腻如玉。可坐数百人。碧霞之瀑。卧泻七八丈。广可五六亩。潨流四溅。烟雪满
阻之耳。不雨不雾又不风。惬心眺赏。似今日者鲜矣。余乃笑曰俺本仙耳。山灵岂阻仙哉。相与一噱。夕还至摩诃。又前数里许下。有深潭泓渟霮䨴。其色黛黑。其名曰火龙。松杉枫栝。荫映于其上。其下有曰船曰龟真珠碧霞喷雪青龙黑龙之号凡八潭。船与龟以其形似之也。珠雪霞以其色似之也。三龙不知所取义。而似以其水最深龙居之也。八潭之下。是为万瀑洞。自火龙至此上下几十里。左右峰峦壁立数千仞。如削铁累棋。巉巉对峙。作一洞天。众壑之水。交注其中。奔腾激射。浤浤汩汩。徐者为潭。急者为瀑。瀑与潭又必相承若贯珠。疾雷骤雨。清瑟哀筑。前唱后喁于十里之中。接袂对面而语。不高声不相闻。一洞全以石成。其高者为山。仄者为路。下者为水之所行而有浅有深。立者为岩。铺者为磐。磊落磅礴。奇峭怪诡。万态备焉。而无有片土错其间。诚天下绝胜界也。未知吴越山水。有能俪此者否也。船潭有石如船。水盈船乃流。龟潭潭上之石酷类龟伏头压于水。真珠之瀑悬流十尺。下触崖窾。飞沫乱跳。迸若珠玑。其声琮琤可听。上有大石盘陀。平广莹腻如玉。可坐数百人。碧霞之瀑。卧泻七八丈。广可五六亩。潨流四溅。烟雪满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5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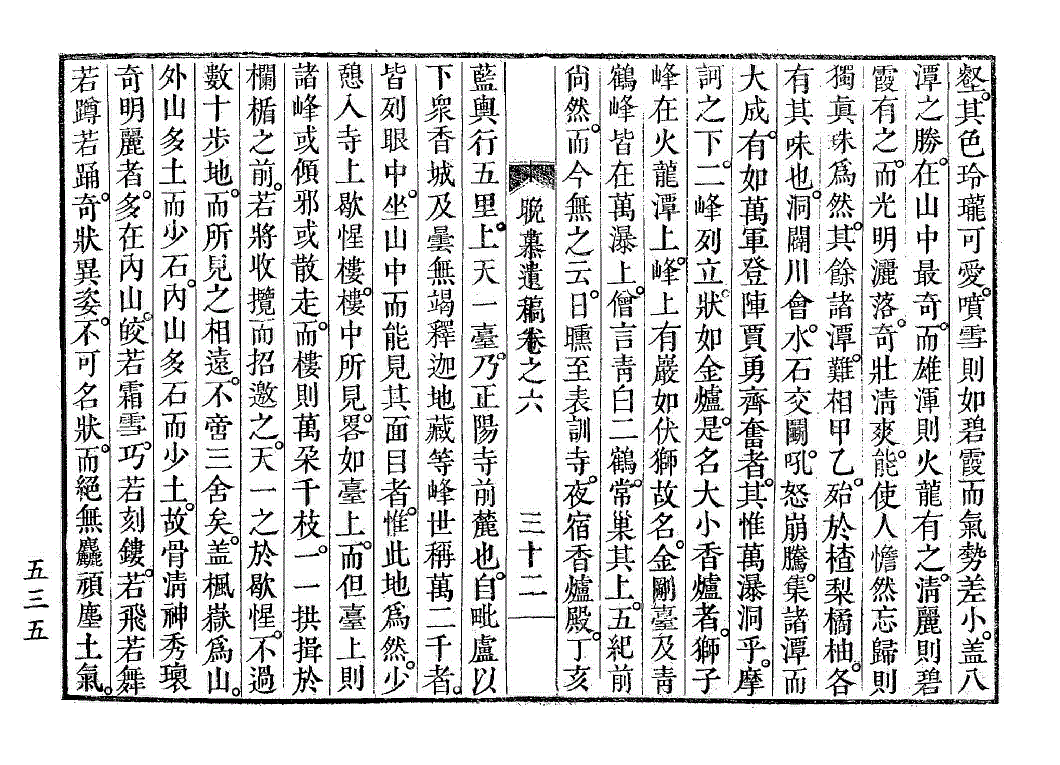 壑。其色玲珑可爱。喷雪则如碧霞而气势差小。盖八潭之胜。在山中最奇。而雄浑则火龙有之。清丽则碧霞有之。而光明洒落。奇壮清爽。能使人憺然忘归则独真珠为然。其馀诸潭。难相甲乙。殆于楂梨橘柚。各有其味也。洞辟川会。水石交斗。吼怒崩腾。集诸潭而大成。有如万军登阵贾勇齐奋者。其惟万瀑洞乎。摩诃之下。二峰列立。状如金炉。是名大小香炉者。狮子峰在火龙潭上。峰上有岩如伏狮故名。金刚台及青鹤峰皆在万瀑上。僧言青白二鹤。常巢其上。五纪前尚然。而今无之云。日曛至表训寺。夜宿香炉殿。丁亥蓝舆行五里。上天一台。乃正阳寺前麓也。自毗卢以下众香城及昙无竭释迦地藏等峰世称万二千者。皆列眼中。坐山中而能见其面目者。惟此地为然。少憩入寺上歇惺楼。楼中所见。略如台上。而但台上则诸峰或倾邪或散走。而楼则万朵千枝。一一拱揖于栏楯之前。若将收揽而招邀之。天一之于歇惺。不过数十步地。而所见之相远。不啻三舍矣。盖枫岳为山。外山多土而少石。内山多石而少土。故骨清神秀瑰奇明丽者。多在内山。皎若霜雪。巧若刻镂。若飞若舞若蹲若踊。奇状异姿。不可名状。而绝无粗顽尘土气。
壑。其色玲珑可爱。喷雪则如碧霞而气势差小。盖八潭之胜。在山中最奇。而雄浑则火龙有之。清丽则碧霞有之。而光明洒落。奇壮清爽。能使人憺然忘归则独真珠为然。其馀诸潭。难相甲乙。殆于楂梨橘柚。各有其味也。洞辟川会。水石交斗。吼怒崩腾。集诸潭而大成。有如万军登阵贾勇齐奋者。其惟万瀑洞乎。摩诃之下。二峰列立。状如金炉。是名大小香炉者。狮子峰在火龙潭上。峰上有岩如伏狮故名。金刚台及青鹤峰皆在万瀑上。僧言青白二鹤。常巢其上。五纪前尚然。而今无之云。日曛至表训寺。夜宿香炉殿。丁亥蓝舆行五里。上天一台。乃正阳寺前麓也。自毗卢以下众香城及昙无竭释迦地藏等峰世称万二千者。皆列眼中。坐山中而能见其面目者。惟此地为然。少憩入寺上歇惺楼。楼中所见。略如台上。而但台上则诸峰或倾邪或散走。而楼则万朵千枝。一一拱揖于栏楯之前。若将收揽而招邀之。天一之于歇惺。不过数十步地。而所见之相远。不啻三舍矣。盖枫岳为山。外山多土而少石。内山多石而少土。故骨清神秀瑰奇明丽者。多在内山。皎若霜雪。巧若刻镂。若飞若舞若蹲若踊。奇状异姿。不可名状。而绝无粗顽尘土气。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6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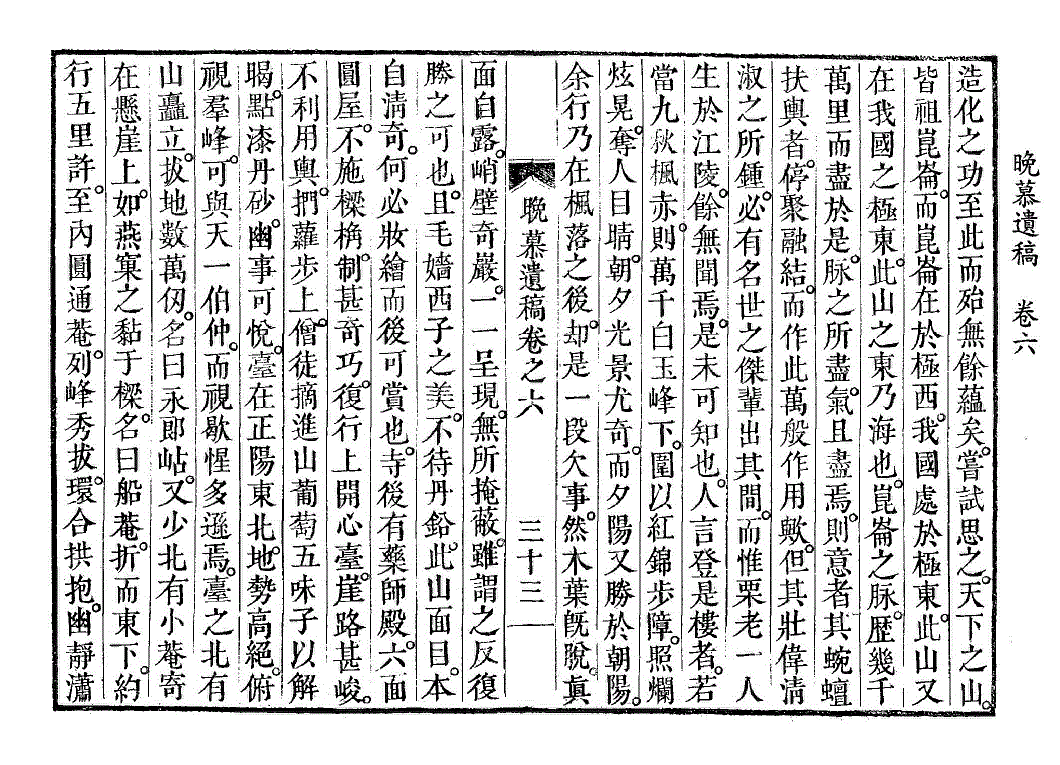 造化之功至此而殆无馀蕴矣。尝试思之。天下之山。皆祖昆崙。而昆崙在于极西。我国处于极东。此山又在我国之极东。此山之东乃海也。昆崙之脉。历几千万里而尽于是。脉之所尽。气且尽焉。则意者其蜿蟺扶舆者。停聚融结。而作此万般作用欤。但其壮伟清淑之所钟。必有名世之杰辈出其间。而惟栗老一人生于江陵。馀无闻焉。是未可知也。人言登是楼者。若当九秋枫赤。则万千白玉峰下。围以红锦步障。照烂炫晃。夺人目睛。朝夕光景尤奇。而夕阳又胜于朝阳。余行乃在枫落之后。却是一段欠事。然木叶既脱。真面自露。峭壁奇岩。一一呈现。无所掩蔽。虽谓之反复胜之可也。且毛嫱西子之美。不待丹铅。此山面目。本自清奇。何必妆绘而后可赏也。寺后有药师殿。六面圆屋。不施梁桷。制甚奇巧。复行上开心台。崖路甚峻。不利用舆。扪萝步上。僧徒摘进山葡萄五味子以解暍。点漆丹砂。幽事可悦。台在正阳东北。地势高绝。俯视群峰。可与天一伯仲。而视歇惺多逊焉。台之北有山矗立。拔地数万仞。名曰永郎岾。又少北有小庵寄在悬崖上。如燕窠之黏于梁。名曰船庵。折而东下。约行五里许。至内圆通庵。列峰秀拔。环合拱抱。幽静潇
造化之功至此而殆无馀蕴矣。尝试思之。天下之山。皆祖昆崙。而昆崙在于极西。我国处于极东。此山又在我国之极东。此山之东乃海也。昆崙之脉。历几千万里而尽于是。脉之所尽。气且尽焉。则意者其蜿蟺扶舆者。停聚融结。而作此万般作用欤。但其壮伟清淑之所钟。必有名世之杰辈出其间。而惟栗老一人生于江陵。馀无闻焉。是未可知也。人言登是楼者。若当九秋枫赤。则万千白玉峰下。围以红锦步障。照烂炫晃。夺人目睛。朝夕光景尤奇。而夕阳又胜于朝阳。余行乃在枫落之后。却是一段欠事。然木叶既脱。真面自露。峭壁奇岩。一一呈现。无所掩蔽。虽谓之反复胜之可也。且毛嫱西子之美。不待丹铅。此山面目。本自清奇。何必妆绘而后可赏也。寺后有药师殿。六面圆屋。不施梁桷。制甚奇巧。复行上开心台。崖路甚峻。不利用舆。扪萝步上。僧徒摘进山葡萄五味子以解暍。点漆丹砂。幽事可悦。台在正阳东北。地势高绝。俯视群峰。可与天一伯仲。而视歇惺多逊焉。台之北有山矗立。拔地数万仞。名曰永郎岾。又少北有小庵寄在悬崖上。如燕窠之黏于梁。名曰船庵。折而东下。约行五里许。至内圆通庵。列峰秀拔。环合拱抱。幽静潇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6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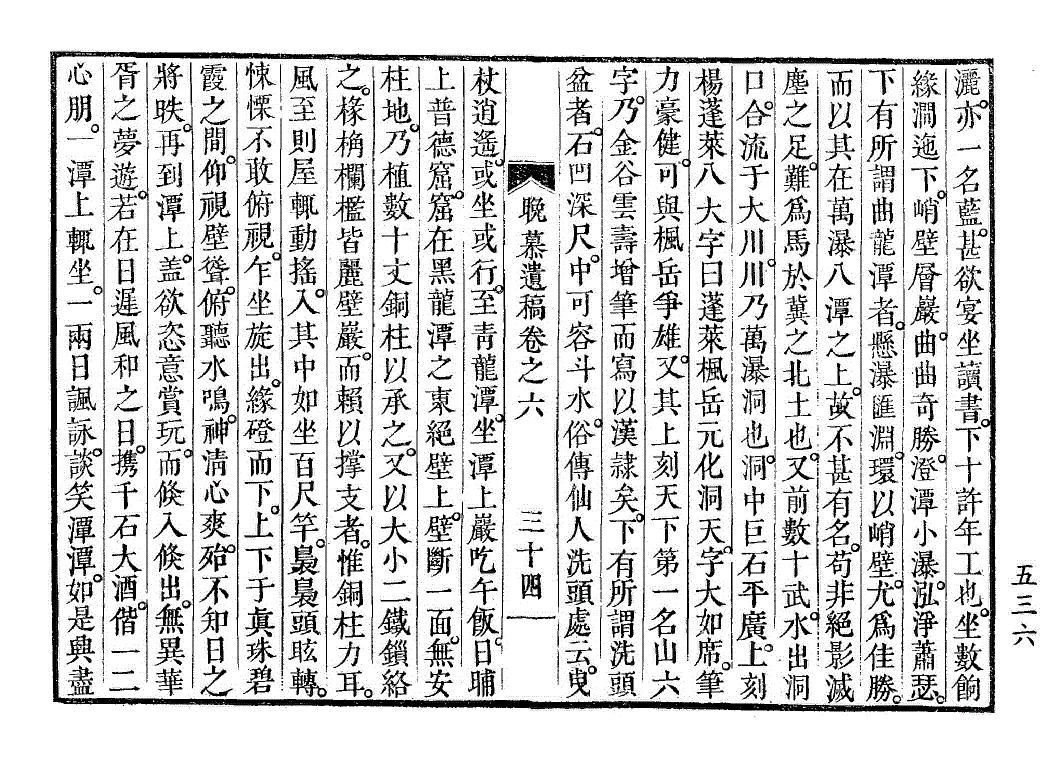 洒。亦一名蓝。甚欲宴坐读书。下十许年工也。坐数饷缘涧迤下。峭壁层岩。曲曲奇胜。澄潭小瀑。泓净萧瑟。下有所谓曲龙潭者。悬瀑汇渊。环以峭壁。尤为佳胜。而以其在万瀑八潭之上。故不甚有名。苟非绝影灭尘之足。难为马于冀之北土也。又前数十武。水出洞口。合流于大川。川乃万瀑洞也。洞中巨石平广。上刻杨蓬莱八大字曰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字大如席。笔力豪健。可与枫岳争雄。又其上刻天下第一名山六字。乃金谷云寿增笔而写以汉隶矣。下有所谓洗头盆者。石凹深尺。中可容斗水。俗传仙人洗头处云。曳杖逍遥。或坐或行。至青龙潭。坐潭上岩吃午饭。日晡上普德窟。窟在黑龙潭之东绝壁上。壁断一面。无安柱地。乃植数十丈铜柱以承之。又以大小二铁锁络之。椽桷栏槛皆丽壁岩。而赖以撑支者。惟铜柱力耳。风至则屋辄动摇。入其中如坐百尺竿。袅袅头眩转。悚慄不敢俯视。乍坐旋出。缘磴而下。上下于真珠碧霞之间。仰视壁耸。俯听水鸣。神清心爽。殆不知日之将昳。再到潭上。盖欲恣意赏玩。而倏入倏出。无异华胥之梦游。若在日迟风和之日。携千石大酒。偕一二心朋。一潭上辄坐。一两日讽咏。谈笑潭潭。如是兴尽
洒。亦一名蓝。甚欲宴坐读书。下十许年工也。坐数饷缘涧迤下。峭壁层岩。曲曲奇胜。澄潭小瀑。泓净萧瑟。下有所谓曲龙潭者。悬瀑汇渊。环以峭壁。尤为佳胜。而以其在万瀑八潭之上。故不甚有名。苟非绝影灭尘之足。难为马于冀之北土也。又前数十武。水出洞口。合流于大川。川乃万瀑洞也。洞中巨石平广。上刻杨蓬莱八大字曰蓬莱枫岳元化洞天。字大如席。笔力豪健。可与枫岳争雄。又其上刻天下第一名山六字。乃金谷云寿增笔而写以汉隶矣。下有所谓洗头盆者。石凹深尺。中可容斗水。俗传仙人洗头处云。曳杖逍遥。或坐或行。至青龙潭。坐潭上岩吃午饭。日晡上普德窟。窟在黑龙潭之东绝壁上。壁断一面。无安柱地。乃植数十丈铜柱以承之。又以大小二铁锁络之。椽桷栏槛皆丽壁岩。而赖以撑支者。惟铜柱力耳。风至则屋辄动摇。入其中如坐百尺竿。袅袅头眩转。悚慄不敢俯视。乍坐旋出。缘磴而下。上下于真珠碧霞之间。仰视壁耸。俯听水鸣。神清心爽。殆不知日之将昳。再到潭上。盖欲恣意赏玩。而倏入倏出。无异华胥之梦游。若在日迟风和之日。携千石大酒。偕一二心朋。一潭上辄坐。一两日讽咏。谈笑潭潭。如是兴尽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7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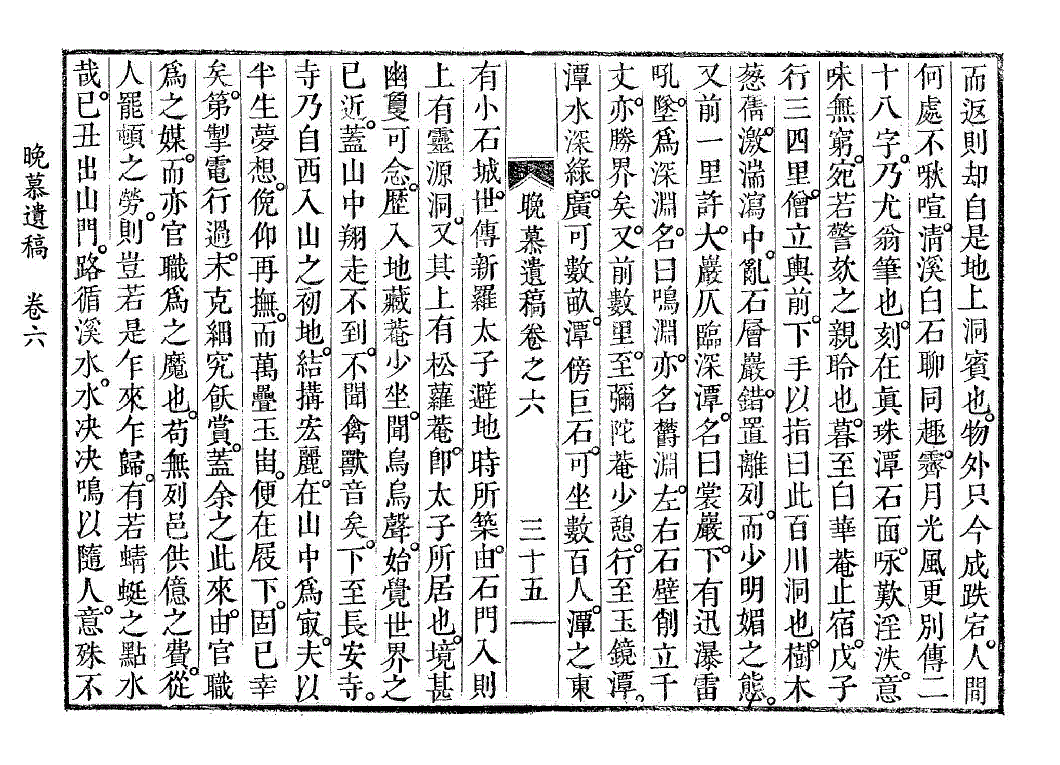 而返则却自是地上洞宾也。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清溪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二十八字。乃尤翁笔也。刻在真珠潭石面。咏叹淫泆。意味无穷。宛若警欬之亲聆也。暮至白华庵止宿。戊子行三四里。僧立舆前。下手以指曰此百川洞也。树木葱茜。激湍泻中。乱石层岩。错置离列。而少明媚之态。又前一里许。大岩仄临深潭。名曰裳岩。下有迅瀑雷吼。坠为深渊。名曰鸣渊。亦名郁渊。左右石壁削立千丈。亦胜界矣。又前数里。至弥陀庵少憩。行至玉镜潭。潭水深绿。广可数亩。潭傍巨石。可坐数百人。潭之东有小石城。世传新罗太子避地时所筑。由石门入则上有灵源洞。又其上有松萝庵。即太子所居也。境甚幽夐可念。历入地藏庵少坐。闻鸟乌声。始觉世界之已近。盖山中翔走不到。不闻禽兽音矣。下至长安寺。寺乃自西入山之初地。结搆宏丽。在山中为最。夫以半生梦想。俛仰再抚。而万叠玉岫。便在屐下。固已幸矣。第掣电行过。未克细究饫赏。盖余之此来。由官职为之媒。而亦官职为之魔也。苟无列邑供亿之费。从人罢顿之劳。则岂若是乍来乍归。有若蜻蜓之点水哉。己丑出山门。路循溪水。水决决鸣以随人。意殊不
而返则却自是地上洞宾也。物外只今成跌宕。人间何处不啾喧。清溪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二十八字。乃尤翁笔也。刻在真珠潭石面。咏叹淫泆。意味无穷。宛若警欬之亲聆也。暮至白华庵止宿。戊子行三四里。僧立舆前。下手以指曰此百川洞也。树木葱茜。激湍泻中。乱石层岩。错置离列。而少明媚之态。又前一里许。大岩仄临深潭。名曰裳岩。下有迅瀑雷吼。坠为深渊。名曰鸣渊。亦名郁渊。左右石壁削立千丈。亦胜界矣。又前数里。至弥陀庵少憩。行至玉镜潭。潭水深绿。广可数亩。潭傍巨石。可坐数百人。潭之东有小石城。世传新罗太子避地时所筑。由石门入则上有灵源洞。又其上有松萝庵。即太子所居也。境甚幽夐可念。历入地藏庵少坐。闻鸟乌声。始觉世界之已近。盖山中翔走不到。不闻禽兽音矣。下至长安寺。寺乃自西入山之初地。结搆宏丽。在山中为最。夫以半生梦想。俛仰再抚。而万叠玉岫。便在屐下。固已幸矣。第掣电行过。未克细究饫赏。盖余之此来。由官职为之媒。而亦官职为之魔也。苟无列邑供亿之费。从人罢顿之劳。则岂若是乍来乍归。有若蜻蜓之点水哉。己丑出山门。路循溪水。水决决鸣以随人。意殊不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7L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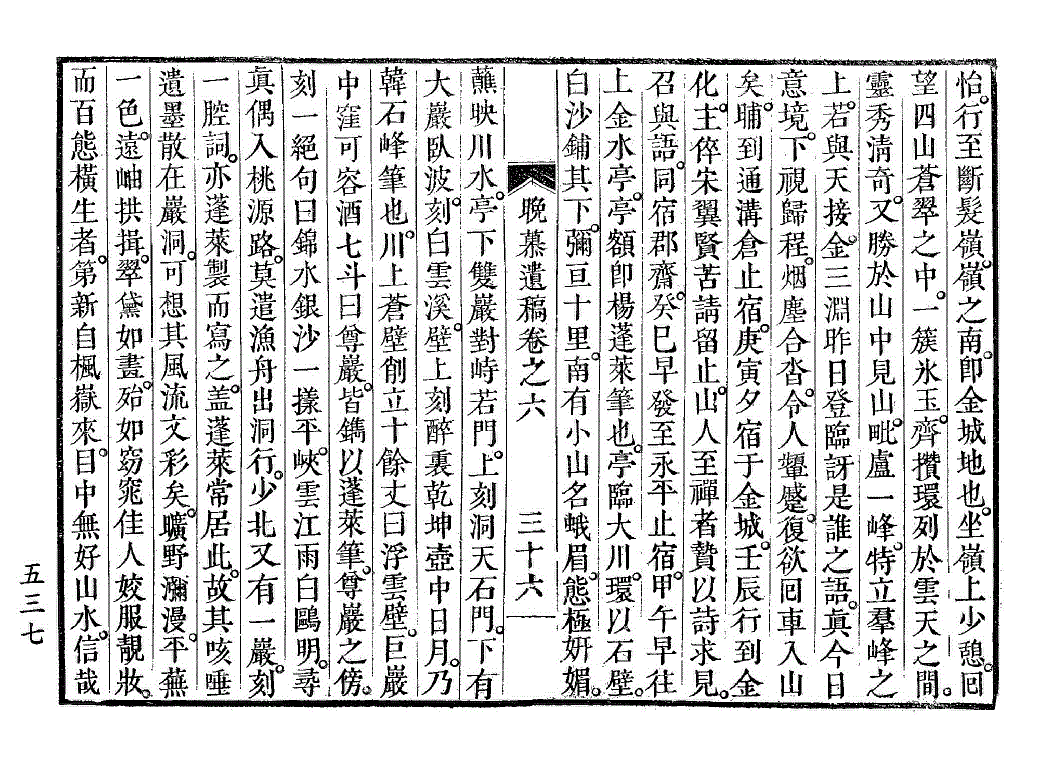 怡。行至断发岭。岭之南。即金城地也。坐岭上少憩。回望四山苍翠之中。一簇冰玉。齐攒环列于云天之间。灵秀清奇。又胜于山中见山。毗卢一峰。特立群峰之上。若与天接。金三渊昨日登临讶是谁之语。真今日意境。下视归程。烟尘合沓。令人颦蹙。复欲回车入山矣。晡到通沟仓止宿。庚寅夕宿于金城。壬辰行到金化。主倅宋翼贤苦请留止。山人至禅者贽以诗求见。召与语。同宿郡斋。癸巳早发至永平止宿。甲午早往上金水亭。亭额即杨蓬莱笔也。亭临大川。环以石壁。白沙铺其下。弥亘十里。南有小山名蛾眉。态极妍媚。蘸映川水。亭下双岩对峙若门。上刻洞天石门。下有大岩卧波。刻白云溪。壁上刻醉里乾坤壶中日月。乃韩石峰笔也。川上苍壁削立十馀丈曰浮云壁。巨岩中洼可容酒七斗曰尊岩。皆镌以蓬莱笔。尊岩之傍。刻一绝句曰锦水银沙一㨾平。峡云江雨白鸥明。寻真偶入桃源路。莫遣渔舟出洞行。少北又有一岩。刻一腔词。亦蓬莱制而写之。盖蓬莱常居此。故其咳唾遗墨散在岩洞。可想其风流文彩矣。旷野瀰漫。平芜一色。远岫拱揖。翠黛如画。殆如窈窕佳人姣服靓妆。而百态横生者。第新自枫岳来。目中无好山水。信哉
怡。行至断发岭。岭之南。即金城地也。坐岭上少憩。回望四山苍翠之中。一簇冰玉。齐攒环列于云天之间。灵秀清奇。又胜于山中见山。毗卢一峰。特立群峰之上。若与天接。金三渊昨日登临讶是谁之语。真今日意境。下视归程。烟尘合沓。令人颦蹙。复欲回车入山矣。晡到通沟仓止宿。庚寅夕宿于金城。壬辰行到金化。主倅宋翼贤苦请留止。山人至禅者贽以诗求见。召与语。同宿郡斋。癸巳早发至永平止宿。甲午早往上金水亭。亭额即杨蓬莱笔也。亭临大川。环以石壁。白沙铺其下。弥亘十里。南有小山名蛾眉。态极妍媚。蘸映川水。亭下双岩对峙若门。上刻洞天石门。下有大岩卧波。刻白云溪。壁上刻醉里乾坤壶中日月。乃韩石峰笔也。川上苍壁削立十馀丈曰浮云壁。巨岩中洼可容酒七斗曰尊岩。皆镌以蓬莱笔。尊岩之傍。刻一绝句曰锦水银沙一㨾平。峡云江雨白鸥明。寻真偶入桃源路。莫遣渔舟出洞行。少北又有一岩。刻一腔词。亦蓬莱制而写之。盖蓬莱常居此。故其咳唾遗墨散在岩洞。可想其风流文彩矣。旷野瀰漫。平芜一色。远岫拱揖。翠黛如画。殆如窈窕佳人姣服靓妆。而百态横生者。第新自枫岳来。目中无好山水。信哉晚慕遗稿卷之六 第 538H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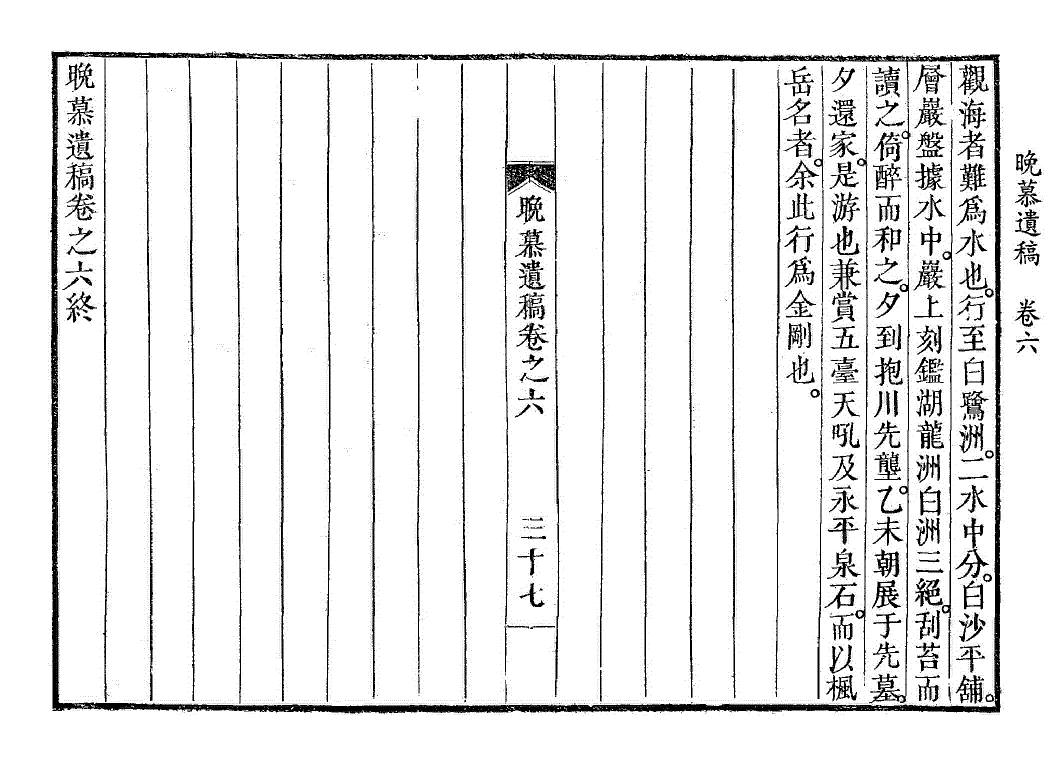 观海者难为水也。行至白鹭洲。二水中分。白沙平铺。层岩盘据水中。岩上刻鉴湖龙洲白洲三绝。刮苔而读之。倚醉而和之。夕到抱川先垄。乙未朝展于先墓。夕还家。是游也兼赏五台天吼及永平泉石。而以枫岳名者。余此行为金刚也。
观海者难为水也。行至白鹭洲。二水中分。白沙平铺。层岩盘据水中。岩上刻鉴湖龙洲白洲三绝。刮苔而读之。倚醉而和之。夕到抱川先垄。乙未朝展于先墓。夕还家。是游也兼赏五台天吼及永平泉石。而以枫岳名者。余此行为金刚也。